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x 页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疏
疏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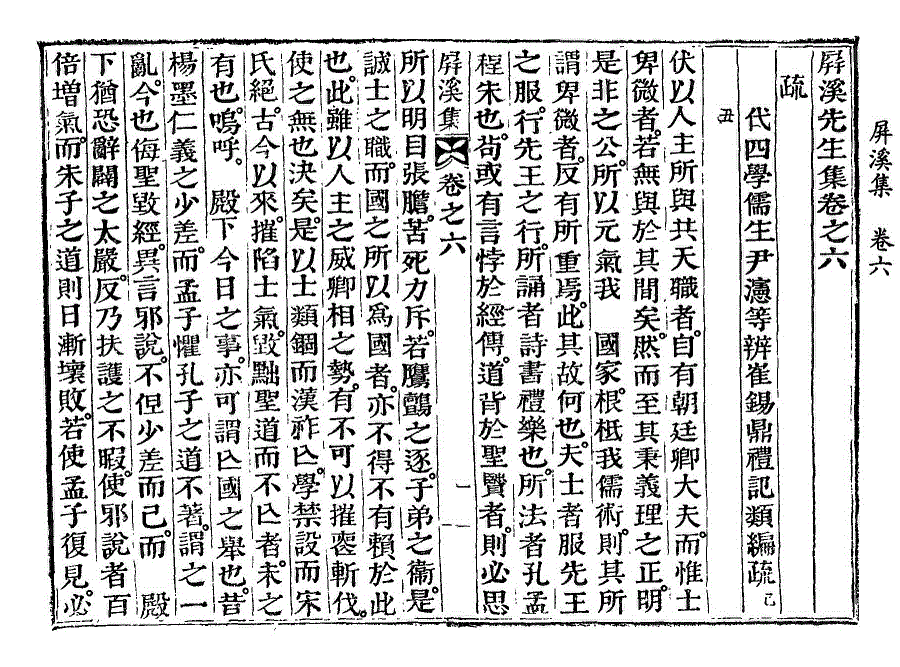 代四学儒生尹瀗等辨崔锡鼎礼记类编疏(己丑)
代四学儒生尹瀗等辨崔锡鼎礼记类编疏(己丑)伏以人主所与共天职者。自有朝廷卿大夫。而惟士卑微者。若无与于其间矣。然而至其秉义理之正。明是非之公。所以元气我 国家。根柢我儒术。则其所谓卑微者。反有所重焉。此其故何也。夫士者服先王之服。行先王之行。所诵者诗书礼乐也。所法者孔孟程朱也。苟或有言悖于经传。道背于圣贤者。则必思所以明目张胆。苦死力斥。若鹰鹯之逐。子弟之卫。是诚士之职。而国之所以为国者。亦不得不有赖于此也。此虽以人主之威卿相之势。有不可以摧丧斩伐。使之无也决矣。是以士类锢而汉祚亡。学禁设而宋氏绝。古今以来。摧陷士气。毁黜圣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呜呼。 殿下今日之事。亦可谓亡国之举也。昔杨墨仁义之少差。而孟子惧孔子之道不著。谓之一乱。今也侮圣毁经。异言邪说。不但少差而已。而 殿下犹恐辞辟之太严。反乃扶护之不暇。使邪说者百倍增气。而朱子之道则日渐坏败。若使孟子复见。必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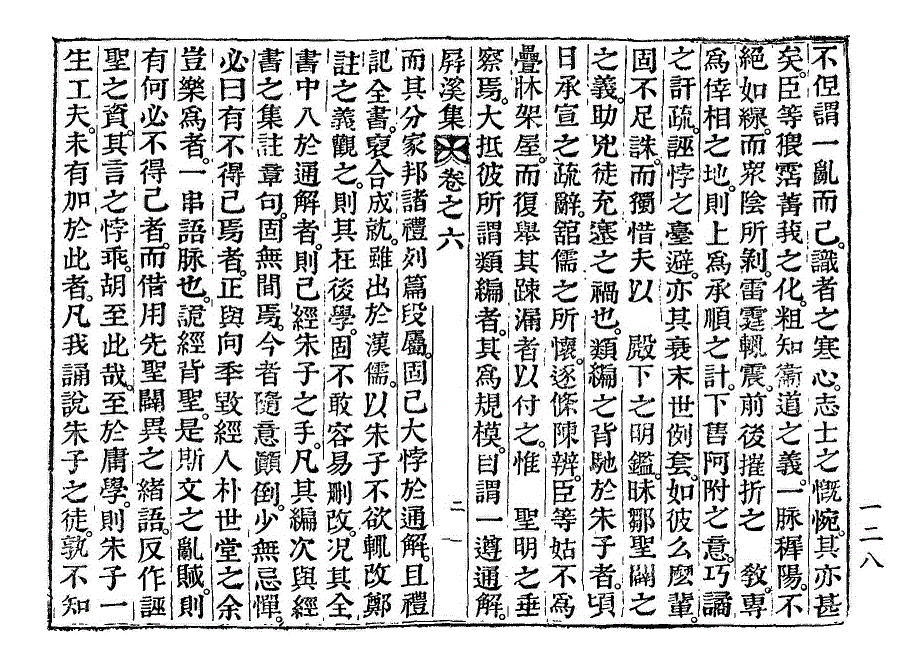 不但谓一乱而已。识者之寒心。志士之慨惋。其亦甚矣。臣等猥沾菁莪之化。粗知卫道之义。一脉稚阳。不绝如线。而众阴所剥。雷霆辄震。前后摧折之 教。专为倖相之地。则上为承顺之计。下售阿附之意。巧谲之讦疏。诬悖之台避。亦其衰末世例套。如彼幺么辈。固不足诛。而独惜夫以 殿下之明鉴。昧邹圣辟之之义。助凶徒充塞之祸也。类编之背驰于朱子者。顷日承宣之疏辞。馆儒之所怀。逐条陈辨。臣等姑不为叠床架屋。而复举其疏漏者以付之。惟 圣明之垂察焉。大抵彼所谓类编者。其为规模。自谓一遵通解。而其分家邦诸礼列篇段属。固已大悖于通解。且礼记全书。裒合成就。虽出于汉儒。以朱子不欲辄改郑注之义观之。则其在后学。固不敢容易删改。况其全书中入于通解者。则已经朱子之手。凡其编次与经书之集注章句。固无间焉。今者随意颠倒。少无忌惮。必曰有不得已焉者。正与向年毁经人朴世堂之余岂乐为者。一串语脉也。诡经背圣。是斯文之乱贼。则有何必不得已者。而借用先圣辟异之绪语。反作诬圣之资。其言之悖乖。胡至此哉。至于庸学。则朱子一生工夫。未有加于此者。凡我诵说朱子之徒。孰不知
不但谓一乱而已。识者之寒心。志士之慨惋。其亦甚矣。臣等猥沾菁莪之化。粗知卫道之义。一脉稚阳。不绝如线。而众阴所剥。雷霆辄震。前后摧折之 教。专为倖相之地。则上为承顺之计。下售阿附之意。巧谲之讦疏。诬悖之台避。亦其衰末世例套。如彼幺么辈。固不足诛。而独惜夫以 殿下之明鉴。昧邹圣辟之之义。助凶徒充塞之祸也。类编之背驰于朱子者。顷日承宣之疏辞。馆儒之所怀。逐条陈辨。臣等姑不为叠床架屋。而复举其疏漏者以付之。惟 圣明之垂察焉。大抵彼所谓类编者。其为规模。自谓一遵通解。而其分家邦诸礼列篇段属。固已大悖于通解。且礼记全书。裒合成就。虽出于汉儒。以朱子不欲辄改郑注之义观之。则其在后学。固不敢容易删改。况其全书中入于通解者。则已经朱子之手。凡其编次与经书之集注章句。固无间焉。今者随意颠倒。少无忌惮。必曰有不得已焉者。正与向年毁经人朴世堂之余岂乐为者。一串语脉也。诡经背圣。是斯文之乱贼。则有何必不得已者。而借用先圣辟异之绪语。反作诬圣之资。其言之悖乖。胡至此哉。至于庸学。则朱子一生工夫。未有加于此者。凡我诵说朱子之徒。孰不知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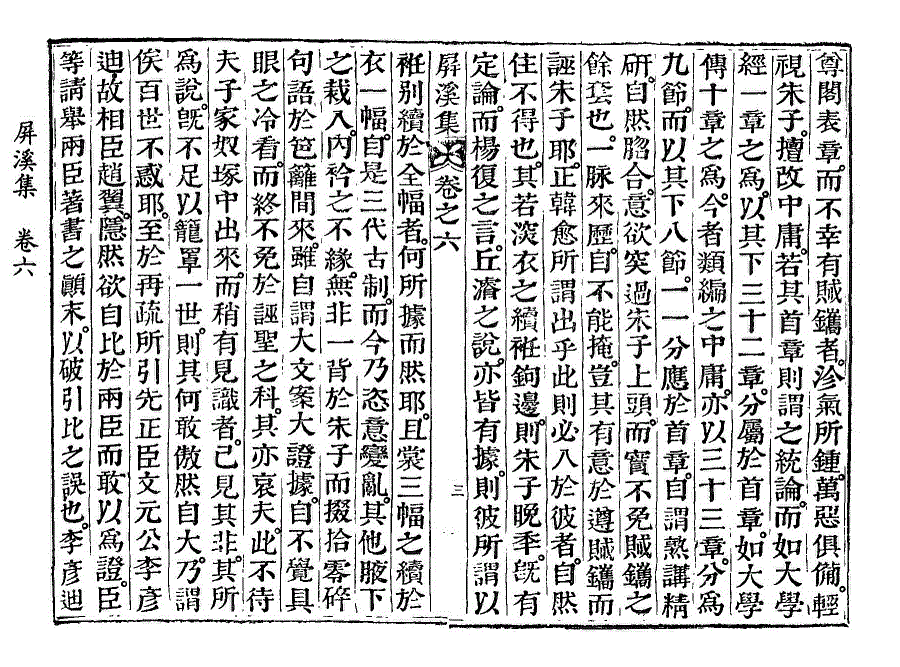 尊阁表章。而不幸有贼鑴者。沴气所钟。万恶俱备。轻视朱子。擅改中庸。若其首章则谓之统论。而如大学经一章之为。以其下三十二章。分属于首章。如大学传十章之为。今者类编之中庸。亦以三十三章。分为九节。而以其下八节。一一分应于首章。自谓熟讲精研。自然吻合。意欲突过朱子上头。而实不免贼鑴之馀套也。一脉来历。自不能掩。岂其有意于遵贼鑴而诬朱子耶。正韩愈所谓出乎此则必入于彼者。自然住不得也。其若深衣之续衽钩边。则朱子晚年。既有定论。而杨复之言。丘浚之说。亦皆有据。则彼所谓以衽别续于全幅者。何所据而然耶。且裳三幅之续于衣一幅。自是三代古制。而今乃恣意变乱。其他腋下之裁入。内衿之不缘。无非一背于朱子而掇拾零碎句语于笆篱间来。虽自谓大文案大證据。自不觉具眼之冷看。而终不免于诬圣之科。其亦哀夫。此不待夫子家奴冢中出来。而稍有见识者。已见其非。其所为说。既不足以笼罩一世。则其何敢傲然自大。乃谓俟百世不惑耶。至于再疏所引先正臣文元公李彦迪,故相臣赵翼。隐然欲自比于两臣而敢以为證。臣等请举两臣著书之颠末。以破引比之误也。李彦迪
尊阁表章。而不幸有贼鑴者。沴气所钟。万恶俱备。轻视朱子。擅改中庸。若其首章则谓之统论。而如大学经一章之为。以其下三十二章。分属于首章。如大学传十章之为。今者类编之中庸。亦以三十三章。分为九节。而以其下八节。一一分应于首章。自谓熟讲精研。自然吻合。意欲突过朱子上头。而实不免贼鑴之馀套也。一脉来历。自不能掩。岂其有意于遵贼鑴而诬朱子耶。正韩愈所谓出乎此则必入于彼者。自然住不得也。其若深衣之续衽钩边。则朱子晚年。既有定论。而杨复之言。丘浚之说。亦皆有据。则彼所谓以衽别续于全幅者。何所据而然耶。且裳三幅之续于衣一幅。自是三代古制。而今乃恣意变乱。其他腋下之裁入。内衿之不缘。无非一背于朱子而掇拾零碎句语于笆篱间来。虽自谓大文案大證据。自不觉具眼之冷看。而终不免于诬圣之科。其亦哀夫。此不待夫子家奴冢中出来。而稍有见识者。已见其非。其所为说。既不足以笼罩一世。则其何敢傲然自大。乃谓俟百世不惑耶。至于再疏所引先正臣文元公李彦迪,故相臣赵翼。隐然欲自比于两臣而敢以为證。臣等请举两臣著书之颠末。以破引比之误也。李彦迪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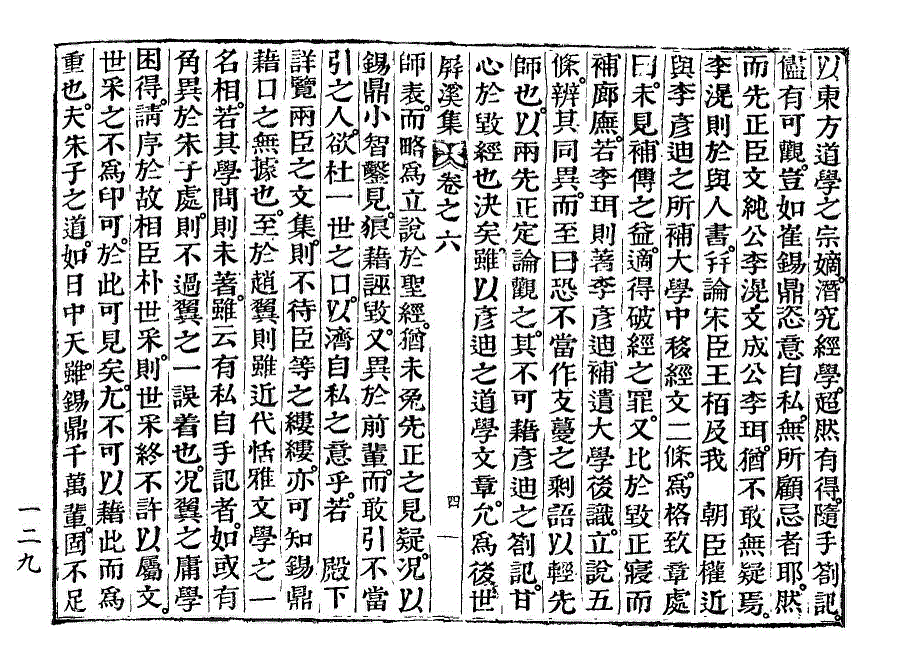 以东方道学之宗嫡。潜究经学。超然有得。随手劄记。尽有可观。岂如崔锡鼎恣意自私。无所顾忌者耶。然而先正臣文纯公李滉,文成公李珥。犹不敢无疑焉。李滉则于与人书。并论宋臣王柏及我 朝臣权近与李彦迪之所补大学中移经文二条。为格致章处曰。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又比于毁正寝而补廊庑。若李珥则著李彦迪补遗大学后识。立说五条。辨其同异。而至曰恐不当作支蔓之剩语以轻先师也。以两先正定论观之。其不可藉彦迪之劄记。甘心于毁经也决矣。虽以彦迪之道学文章。允为后世师表。而略为立说于圣经。犹未免先正之见疑。况以锡鼎小智凿见。狼藉诬毁。又异于前辈。而敢引不当引之人。欲杜一世之口。以济自私之意乎。若 殿下详览两臣之文集。则不待臣等之缕缕。亦可知锡鼎藉口之无据也。至于赵翼则虽近代恬雅文学之一名相。若其学问则未著。虽云有私自手记者。如或有角异于朱子处。则不过翼之一误着也。况翼之庸学困得。请序于故相臣朴世采。则世采终不许以属文。世采之不为印可。于此可见矣。尤不可以藉此而为重也。夫朱子之道。如日中天。虽锡鼎千万辈。固不足
以东方道学之宗嫡。潜究经学。超然有得。随手劄记。尽有可观。岂如崔锡鼎恣意自私。无所顾忌者耶。然而先正臣文纯公李滉,文成公李珥。犹不敢无疑焉。李滉则于与人书。并论宋臣王柏及我 朝臣权近与李彦迪之所补大学中移经文二条。为格致章处曰。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又比于毁正寝而补廊庑。若李珥则著李彦迪补遗大学后识。立说五条。辨其同异。而至曰恐不当作支蔓之剩语以轻先师也。以两先正定论观之。其不可藉彦迪之劄记。甘心于毁经也决矣。虽以彦迪之道学文章。允为后世师表。而略为立说于圣经。犹未免先正之见疑。况以锡鼎小智凿见。狼藉诬毁。又异于前辈。而敢引不当引之人。欲杜一世之口。以济自私之意乎。若 殿下详览两臣之文集。则不待臣等之缕缕。亦可知锡鼎藉口之无据也。至于赵翼则虽近代恬雅文学之一名相。若其学问则未著。虽云有私自手记者。如或有角异于朱子处。则不过翼之一误着也。况翼之庸学困得。请序于故相臣朴世采。则世采终不许以属文。世采之不为印可。于此可见矣。尤不可以藉此而为重也。夫朱子之道。如日中天。虽锡鼎千万辈。固不足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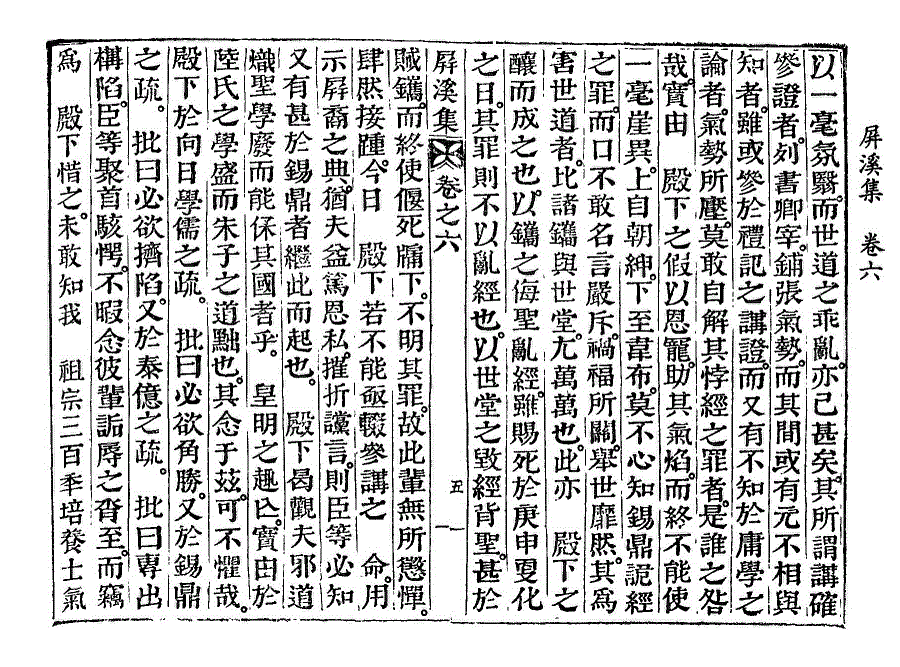 以一毫氛翳。而世道之乖乱。亦已甚矣。其所谓讲确参證者。列书卿宰。铺张气势。而其间或有元不相与知者。虽或参于礼记之讲證。而又有不知于庸学之论者。气势所压。莫敢自解其悖经之罪者。是谁之咎哉。实由 殿下之假以恩宠。助其气焰。而终不能使一毫崖异。上自朝绅。下至韦布。莫不心知锡鼎诡经之罪。而口不敢名言严斥。祸福所关。举世靡然。其为害世道者。比诸鑴与世堂。尤万万也。此亦 殿下之酿而成之也。以鑴之侮圣乱经。虽赐死于庚申更化之日。其罪则不以乱经也。以世堂之毁经背圣。甚于贼鑴。而终使偃死牖下。不明其罪。故此辈无所惩惮。肆然接踵。今日 殿下若不能亟辍参讲之 命。用示屏裔之典。犹夫益笃恩私。摧折谠言。则臣等必知又有甚于锡鼎者继此而起也。 殿下曷观夫邪道炽圣学废而能保其国者乎。 皇明之趣亡。实由于陆氏之学盛而朱子之道黜也。其念于兹。可不惧哉。殿下于向日学儒之疏。 批曰必欲角胜。又于锡鼎之疏。 批曰必欲挤陷。又于泰亿之疏。 批曰专出构陷。臣等聚首骇愕。不暇念彼辈诟辱之沓至。而窃为 殿下惜之。未敢知我 祖宗三百年培养士气
以一毫氛翳。而世道之乖乱。亦已甚矣。其所谓讲确参證者。列书卿宰。铺张气势。而其间或有元不相与知者。虽或参于礼记之讲證。而又有不知于庸学之论者。气势所压。莫敢自解其悖经之罪者。是谁之咎哉。实由 殿下之假以恩宠。助其气焰。而终不能使一毫崖异。上自朝绅。下至韦布。莫不心知锡鼎诡经之罪。而口不敢名言严斥。祸福所关。举世靡然。其为害世道者。比诸鑴与世堂。尤万万也。此亦 殿下之酿而成之也。以鑴之侮圣乱经。虽赐死于庚申更化之日。其罪则不以乱经也。以世堂之毁经背圣。甚于贼鑴。而终使偃死牖下。不明其罪。故此辈无所惩惮。肆然接踵。今日 殿下若不能亟辍参讲之 命。用示屏裔之典。犹夫益笃恩私。摧折谠言。则臣等必知又有甚于锡鼎者继此而起也。 殿下曷观夫邪道炽圣学废而能保其国者乎。 皇明之趣亡。实由于陆氏之学盛而朱子之道黜也。其念于兹。可不惧哉。殿下于向日学儒之疏。 批曰必欲角胜。又于锡鼎之疏。 批曰必欲挤陷。又于泰亿之疏。 批曰专出构陷。臣等聚首骇愕。不暇念彼辈诟辱之沓至。而窃为 殿下惜之。未敢知我 祖宗三百年培养士气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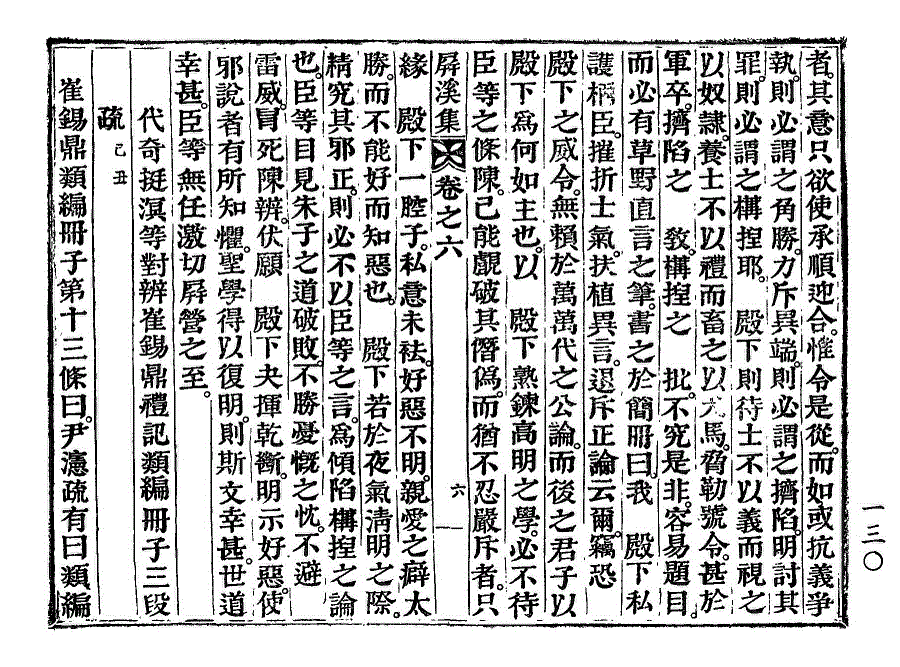 者。其意只欲使承顺迎合。惟令是从。而如或抗义争执。则必谓之角胜。力斥异端。则必谓之挤陷。明讨其罪。则必谓之构捏耶。 殿下则待士不以义而视之以奴隶。养士不以礼而畜之以犬马。胁勒号令。甚于军卒。挤陷之 教。构捏之 批。不究是非。容易题目。而必有草野直言之笔。书之于简册曰。我 殿下私护柄臣。摧折士气。扶植异言。退斥正论云尔。窃恐 殿下之威令。无赖于万万代之公论。而后之君子以殿下为何如主也。以 殿下熟鍊高明之学。必不待臣等之条陈。已能觑破其僭伪。而犹不忍严斥者。只缘 殿下一腔子。私意未袪。好恶不明。亲爱之癖太胜。而不能好而知恶也。 殿下若于夜气清明之际。精究其邪正。则必不以臣等之言。为倾陷构捏之论也。臣等目见朱子之道破败。不胜忧慨之忱。不避 雷威。冒死陈辨。伏愿 殿下夬挥乾断。明示好恶。使邪说者有所知惧。圣学得以复明。则斯文幸甚。世道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者。其意只欲使承顺迎合。惟令是从。而如或抗义争执。则必谓之角胜。力斥异端。则必谓之挤陷。明讨其罪。则必谓之构捏耶。 殿下则待士不以义而视之以奴隶。养士不以礼而畜之以犬马。胁勒号令。甚于军卒。挤陷之 教。构捏之 批。不究是非。容易题目。而必有草野直言之笔。书之于简册曰。我 殿下私护柄臣。摧折士气。扶植异言。退斥正论云尔。窃恐 殿下之威令。无赖于万万代之公论。而后之君子以殿下为何如主也。以 殿下熟鍊高明之学。必不待臣等之条陈。已能觑破其僭伪。而犹不忍严斥者。只缘 殿下一腔子。私意未袪。好恶不明。亲爱之癖太胜。而不能好而知恶也。 殿下若于夜气清明之际。精究其邪正。则必不以臣等之言。为倾陷构捏之论也。臣等目见朱子之道破败。不胜忧慨之忱。不避 雷威。冒死陈辨。伏愿 殿下夬挥乾断。明示好恶。使邪说者有所知惧。圣学得以复明。则斯文幸甚。世道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代奇挺溟等对辨崔锡鼎礼记类编册子三段疏(己丑)
崔锡鼎类编册子第十三条曰。尹瀗疏有曰类编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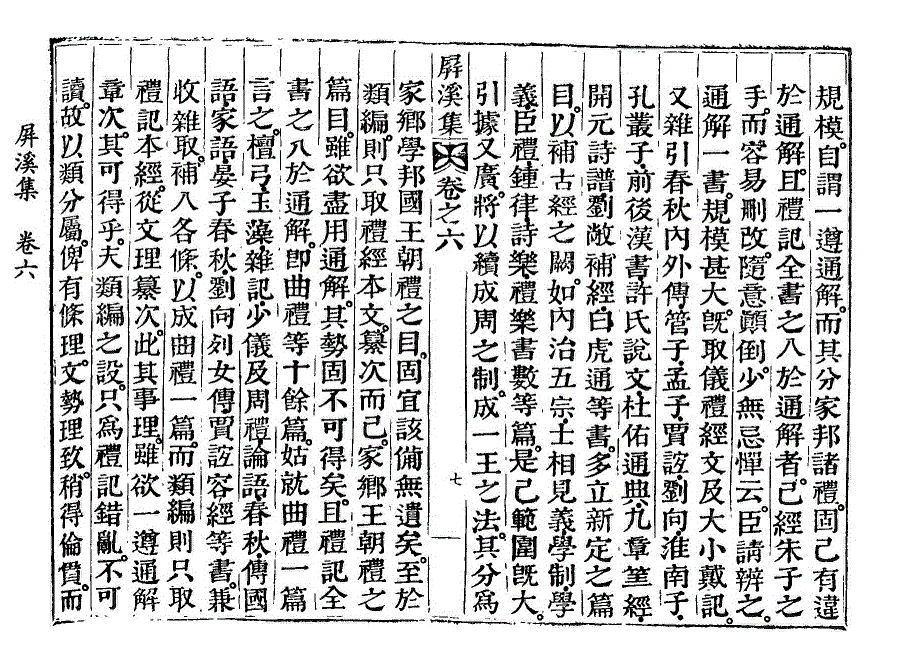 规模。自谓一遵通解。而其分家邦诸礼。固已有违于通解。且礼记全书之入于通解者。已经朱子之手。而容易删改。随意颠倒。少无忌惮云。臣请辨之。通解一书。规模甚大。既取仪礼经文及大小戴记。又杂引春秋内外传,管子,孟子,贾谊,刘向,淮南子,孔丛子,前后汉书,许氏说文,杜佑通典,九章算经,开元诗谱,刘敞补经,白虎通等书。多立新定之篇目。以补古经之阙。如内治五宗,士相见义,学制,学义,臣礼,钟律,诗乐,礼乐书数等篇。是已范围既大。引据又广。将以续成周之制。成一王之法。其分为家乡学邦国王朝礼之目。固宜该备无遗矣。至于类编。则只取礼经本文。纂次而已。家乡王朝礼之篇目。虽欲尽用通解。其势固不可得矣。且礼记全书之入于通解。即曲礼等十馀篇。姑就曲礼一篇言之。檀弓,玉藻,杂记,少仪及周礼,论语,春秋,传国语,家语,晏子春秋,刘向列女传,贾谊容经等书。兼收杂取。补入各条。以成曲礼一篇。而类编则只取礼记本经。从文理纂次。此其事理。虽欲一遵通解章次。其可得乎。夫类编之设。只为礼记错乱。不可读。故以类分属。俾有条理。文势理致。稍得伦贯。而
规模。自谓一遵通解。而其分家邦诸礼。固已有违于通解。且礼记全书之入于通解者。已经朱子之手。而容易删改。随意颠倒。少无忌惮云。臣请辨之。通解一书。规模甚大。既取仪礼经文及大小戴记。又杂引春秋内外传,管子,孟子,贾谊,刘向,淮南子,孔丛子,前后汉书,许氏说文,杜佑通典,九章算经,开元诗谱,刘敞补经,白虎通等书。多立新定之篇目。以补古经之阙。如内治五宗,士相见义,学制,学义,臣礼,钟律,诗乐,礼乐书数等篇。是已范围既大。引据又广。将以续成周之制。成一王之法。其分为家乡学邦国王朝礼之目。固宜该备无遗矣。至于类编。则只取礼经本文。纂次而已。家乡王朝礼之篇目。虽欲尽用通解。其势固不可得矣。且礼记全书之入于通解。即曲礼等十馀篇。姑就曲礼一篇言之。檀弓,玉藻,杂记,少仪及周礼,论语,春秋,传国语,家语,晏子春秋,刘向列女传,贾谊容经等书。兼收杂取。补入各条。以成曲礼一篇。而类编则只取礼记本经。从文理纂次。此其事理。虽欲一遵通解章次。其可得乎。夫类编之设。只为礼记错乱。不可读。故以类分属。俾有条理。文势理致。稍得伦贯。而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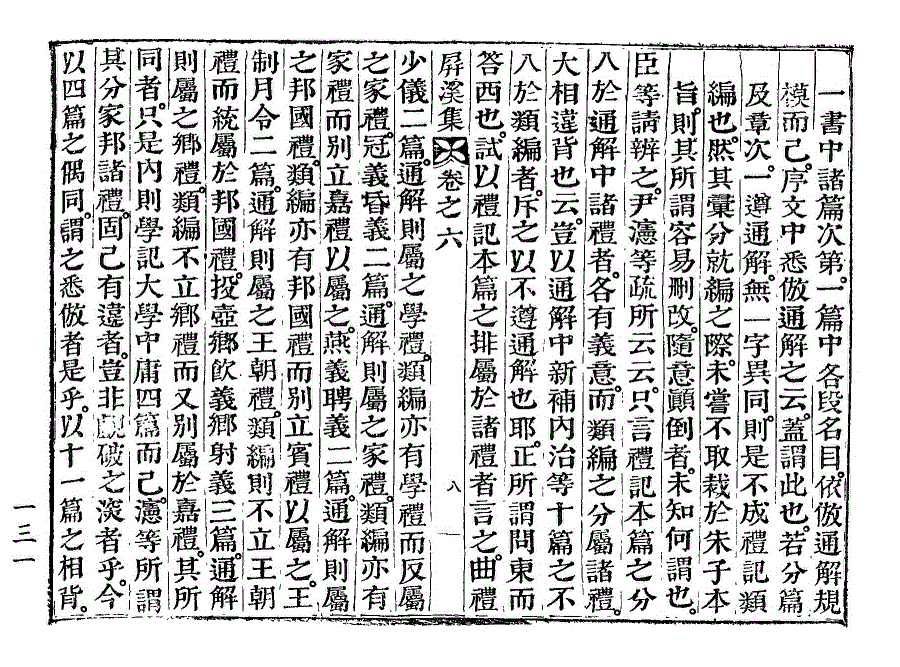 一书中诸篇次第。一篇中各段名目。依仿通解规模而已。序文中悉仿通解之云。盖谓此也。若分篇及章次。一遵通解。无一字异同。则是不成礼记类编也。然其汇分就编之际。未尝不取裁于朱子本旨。则其所谓容易删改。随意颠倒者。未知何谓也。
一书中诸篇次第。一篇中各段名目。依仿通解规模而已。序文中悉仿通解之云。盖谓此也。若分篇及章次。一遵通解。无一字异同。则是不成礼记类编也。然其汇分就编之际。未尝不取裁于朱子本旨。则其所谓容易删改。随意颠倒者。未知何谓也。臣等请辨之。尹瀗等疏所云云。只言礼记本篇之分入于通解中诸礼者。各有义意。而类编之分属诸礼。大相违背也云。岂以通解中新补内治等十篇之不入于类编者。斥之以不遵通解也耶。正所谓问东而答西也。试以礼记本篇之排属于诸礼者言之。曲礼少仪二篇。通解则属之学礼。类编亦有学礼而反属之家礼。冠义昏义二篇。通解则属之家礼。类编亦有家礼而别立嘉礼以属之。燕义聘义二篇。通解则属之邦国礼。类编亦有邦国礼而别立宾礼以属之。王制月令二篇。通解则属之王朝礼。类编则不立王朝礼而统属于邦国礼。投壶乡饮义乡射义三篇。通解则属之乡礼。类编不立乡礼而又别属于嘉礼。其所同者。只是内则学记大学中庸四篇而已。瀗等所谓其分家邦诸礼。固已有违者。岂非觑破之深者乎。今以四篇之偶同。谓之悉仿者是乎。以十一篇之相背。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2H 页
 谓之违异者非乎。两书俱存。其可欺乎。且王制月令。乃天子事。则此非王朝礼而何。然而类编不立王朝礼。而以此两篇统于邦国礼。是天子而见统于诸侯也。其于名分之乖绝。事体之谬异何哉。至以分礼言之。通解则只分家乡学邦国王朝五礼。类编则分为家邦学吉凶嘉宾七礼。其为规模。亦岂不务广于通解者乎。且礼记全书中入于通解者。已经朱子之手而正其章次。则其取用他书处。未必言矣。本篇中小目之名。上下之次。亦不可从朱子勘定耶。以曲礼少仪等诸篇言之。曲礼中某某章。通解则载于某篇。而类编则必移入于他篇。少仪中某某章。通解则载于此。而类编则必移置于彼。个个相反。无一近似。如此之类。如欲毛举。殆成一秩书。烦不敢条陈。瀗等所谓随意颠倒无少忌惮者。亦何可逃也。况其悉举仪礼中引用诸书之名。尤是题外之剩语。此不过出于眩乱人耳目。而不觉识者之冷眼看了。其为遮护外面之计。亦云疏矣。既曰尽用通解。其势不得云。则其曰一书中诸篇第次。一篇中各段名目。依仿通解云者。其上下文势之矛盾。何若是甚也。至于汇分就编。未尝不取裁于朱子本旨云者。尤不成说。即何以异于
谓之违异者非乎。两书俱存。其可欺乎。且王制月令。乃天子事。则此非王朝礼而何。然而类编不立王朝礼。而以此两篇统于邦国礼。是天子而见统于诸侯也。其于名分之乖绝。事体之谬异何哉。至以分礼言之。通解则只分家乡学邦国王朝五礼。类编则分为家邦学吉凶嘉宾七礼。其为规模。亦岂不务广于通解者乎。且礼记全书中入于通解者。已经朱子之手而正其章次。则其取用他书处。未必言矣。本篇中小目之名。上下之次。亦不可从朱子勘定耶。以曲礼少仪等诸篇言之。曲礼中某某章。通解则载于某篇。而类编则必移入于他篇。少仪中某某章。通解则载于此。而类编则必移置于彼。个个相反。无一近似。如此之类。如欲毛举。殆成一秩书。烦不敢条陈。瀗等所谓随意颠倒无少忌惮者。亦何可逃也。况其悉举仪礼中引用诸书之名。尤是题外之剩语。此不过出于眩乱人耳目。而不觉识者之冷眼看了。其为遮护外面之计。亦云疏矣。既曰尽用通解。其势不得云。则其曰一书中诸篇第次。一篇中各段名目。依仿通解云者。其上下文势之矛盾。何若是甚也。至于汇分就编。未尝不取裁于朱子本旨云者。尤不成说。即何以异于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2L 页
 以刃刺人而曰我非杀人者耶。伏乞 圣照。
以刃刺人而曰我非杀人者耶。伏乞 圣照。第十四条。又以为贼鑴擅改中庸。以首章谓之统论。其下三十二章。分属于首章。如大学传十章之为。今类编之中庸。以三十三章。分为九节。其下八节。分应于首节。实不免贼鑴之馀套云。此又虚罔之甚也。鑴之所著中庸说。则以一篇。分为十章二十八节。而其所分章。率多谬戾。类编则三十三章。固自如也。只就饶氏六节。演为九节。上五节。分照统论五段。下三节。分照首段三句。与鑴说不啻悬殊。节节相反。今谓之遵贼鑴而诬朱子何也。且鑴说。只称首章初无统论之目。而今以类编之有统论。强立鑴说所无之目。谬引而混称之。以为眩乱污蔑之计。噫。亦异矣。
臣等请辨之。鑴之擅改中庸章句也。盖以首章。段段分割。为许多纲领。如大学经一章之为。以其下三十二章。分属于首章。如大学传十章之为。彼所谓类编。亦分为九节。而以其下八节。分属首节。如大学传十章之于经一章。其为规模体格。自不免鑴之馀套。而同一心法。则与朱子章句。一切相反。至于分章分节。特其零碎节目。固不必屑屑较辨矣。瀗疏所谓遵贼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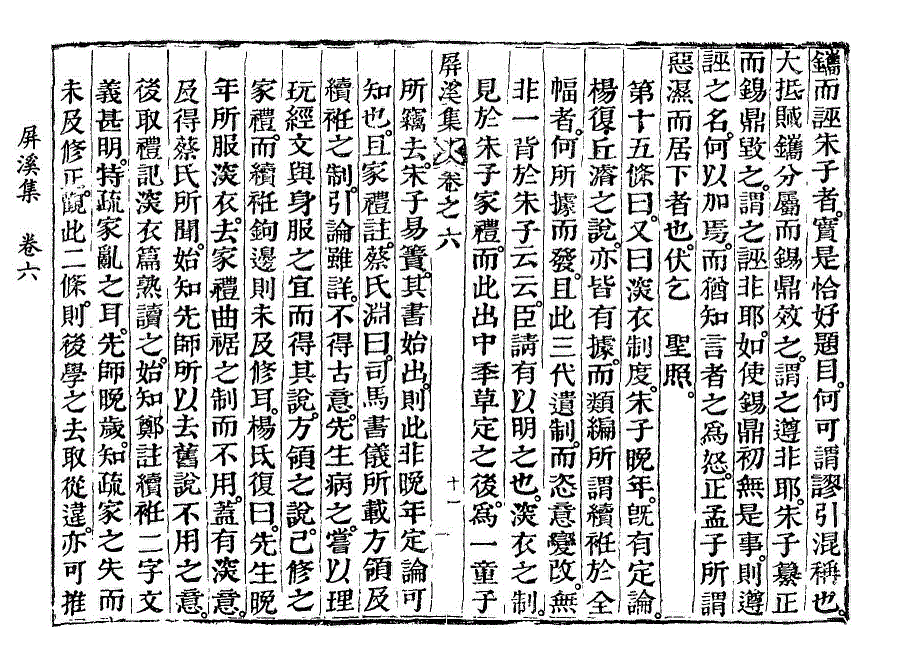 鑴而诬朱子者。实是恰好题目。何可谓谬引混称也。大抵贼鑴分属而锡鼎效之。谓之遵非耶。朱子纂正而锡鼎毁之。谓之诬非耶。如使锡鼎初无是事。则遵诬之名。何以加焉。而犹知言者之为怒。正孟子所谓恶湿而居下者也。伏乞 圣照。
鑴而诬朱子者。实是恰好题目。何可谓谬引混称也。大抵贼鑴分属而锡鼎效之。谓之遵非耶。朱子纂正而锡鼎毁之。谓之诬非耶。如使锡鼎初无是事。则遵诬之名。何以加焉。而犹知言者之为怒。正孟子所谓恶湿而居下者也。伏乞 圣照。第十五条曰。又曰深衣制度。朱子晚年。既有定论。杨复,丘浚之说。亦皆有据。而类编所谓续衽于全幅者。何所据而发。且此三代遗制。而恣意变改。无非一背于朱子云云。臣请有以明之也。深衣之制。见于朱子家礼。而此出中年草定之后。为一童子所窃去。朱子易箦。其书始出。则此非晚年定论可知也。且家礼注。蔡氏渊曰。司马书仪所载方领及续衽之制。引论虽详。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尝以理玩经文与身服之宜而得其说。方领之说。已修之家礼。而续衽钩边则未及修耳。杨氏复曰。先生晚年所服深衣。去家礼曲裾之制而不用。盖有深意。及得蔡氏所闻。始知先师所以去旧说不用之意。后取礼记深衣篇熟读之。始知郑注续衽二字文义甚明。特疏家乱之耳。先师晚岁。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正。观此二条。则后学之去取从违。亦可推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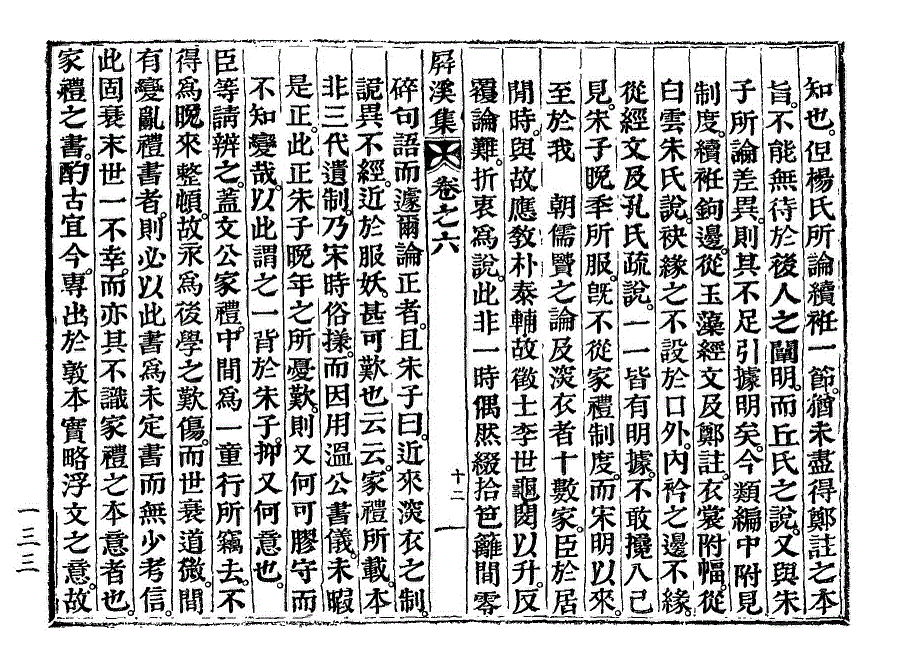 知也。但杨氏所论续衽一节。犹未尽得郑注之本旨。不能无待于后人之阐明。而丘氏之说。又与朱子所论差异。则其不足引据明矣。今类编中附见制度。续衽钩边。从玉藻经文及郑注。衣裳附幅。从白云朱氏说。袂缘之不设于口外。内衿之边不缘。从经文及孔氏疏说。一一皆有明据。不敢搀入己见。朱子晚年所服。既不从家礼制度。而宋明以来。至于我 朝儒贤之论及深衣者十数家。臣于居閒时。与故应教朴泰辅,故徵士李世龟,闵以升。反覆论难。折衷为说。此非一时偶然缀拾笆篱间零碎句语而遽尔论正者。且朱子曰。近来深衣之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云云。家礼所载。本非三代遗制。乃宋时俗㨾。而因用温公书仪。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之所忧叹。则又何可胶守而不知变哉。以此谓之一背于朱子。抑又何意也。
知也。但杨氏所论续衽一节。犹未尽得郑注之本旨。不能无待于后人之阐明。而丘氏之说。又与朱子所论差异。则其不足引据明矣。今类编中附见制度。续衽钩边。从玉藻经文及郑注。衣裳附幅。从白云朱氏说。袂缘之不设于口外。内衿之边不缘。从经文及孔氏疏说。一一皆有明据。不敢搀入己见。朱子晚年所服。既不从家礼制度。而宋明以来。至于我 朝儒贤之论及深衣者十数家。臣于居閒时。与故应教朴泰辅,故徵士李世龟,闵以升。反覆论难。折衷为说。此非一时偶然缀拾笆篱间零碎句语而遽尔论正者。且朱子曰。近来深衣之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云云。家礼所载。本非三代遗制。乃宋时俗㨾。而因用温公书仪。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之所忧叹。则又何可胶守而不知变哉。以此谓之一背于朱子。抑又何意也。臣等请辨之。盖文公家礼。中间为一童行所窃去。不得为晚来整顿。故永为后学之叹伤。而世衰道微。间有变乱礼书者。则必以此书为未定书而无少考信。此固衰末世一不幸。而亦其不识家礼之本意者也。家礼之书。酌古宜今。专出于敦本实略浮文之意。故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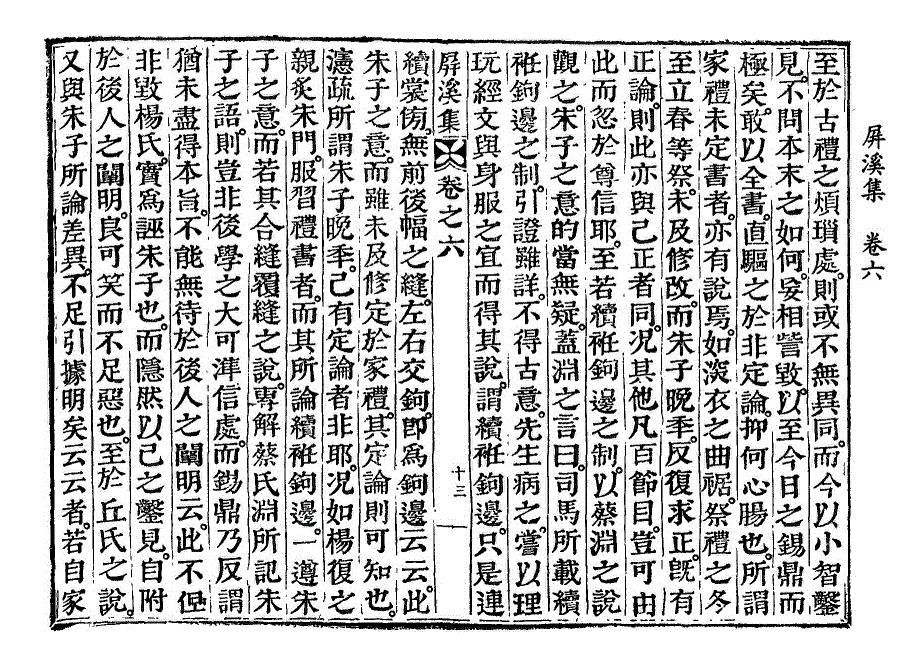 至于古礼之烦琐处。则或不无异同。而今以小智凿见。不问本末之如何。妄相訾毁。以至今日之锡鼎而极矣。敢以全书。直驱之于非定论。抑何心肠也。所谓家礼未定书者。亦有说焉。如深衣之曲裾。祭礼之冬至立春等祭。未及修改。而朱子晚年。反复求正。既有正论。则此亦与已正者同。况其他凡百节目。岂可由此而忽于尊信耶。至若续衽钩边之制。以蔡渊之说观之。朱子之意的当无疑。盖渊之言曰。司马所载续衽钩边之制。引證虽详。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尝以理玩经文与身服之宜而得其说。谓续衽钩边。只是连续裳傍。无前后幅之缝。左右交钩。即为钩边云云。此朱子之意。而虽未及修定于家礼。其定论则可知也。瀗疏所谓朱子晚年。已有定论者非耶。况如杨复之亲炙朱门。服习礼书者。而其所论续衽钩边。一遵朱子之意。而若其合缝覆缝之说。专解蔡氏渊所记朱子之语。则岂非后学之大可准信处。而锡鼎乃反谓犹未尽得本旨。不能无待于后人之阐明云。此不但非毁杨氏。实为诬朱子也。而隐然以己之凿见。自附于后人之阐明。良可笑而不足恶也。至于丘氏之说。又与朱子所论差异。不足引据明矣云云者。若自家
至于古礼之烦琐处。则或不无异同。而今以小智凿见。不问本末之如何。妄相訾毁。以至今日之锡鼎而极矣。敢以全书。直驱之于非定论。抑何心肠也。所谓家礼未定书者。亦有说焉。如深衣之曲裾。祭礼之冬至立春等祭。未及修改。而朱子晚年。反复求正。既有正论。则此亦与已正者同。况其他凡百节目。岂可由此而忽于尊信耶。至若续衽钩边之制。以蔡渊之说观之。朱子之意的当无疑。盖渊之言曰。司马所载续衽钩边之制。引證虽详。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尝以理玩经文与身服之宜而得其说。谓续衽钩边。只是连续裳傍。无前后幅之缝。左右交钩。即为钩边云云。此朱子之意。而虽未及修定于家礼。其定论则可知也。瀗疏所谓朱子晚年。已有定论者非耶。况如杨复之亲炙朱门。服习礼书者。而其所论续衽钩边。一遵朱子之意。而若其合缝覆缝之说。专解蔡氏渊所记朱子之语。则岂非后学之大可准信处。而锡鼎乃反谓犹未尽得本旨。不能无待于后人之阐明云。此不但非毁杨氏。实为诬朱子也。而隐然以己之凿见。自附于后人之阐明。良可笑而不足恶也。至于丘氏之说。又与朱子所论差异。不足引据明矣云云者。若自家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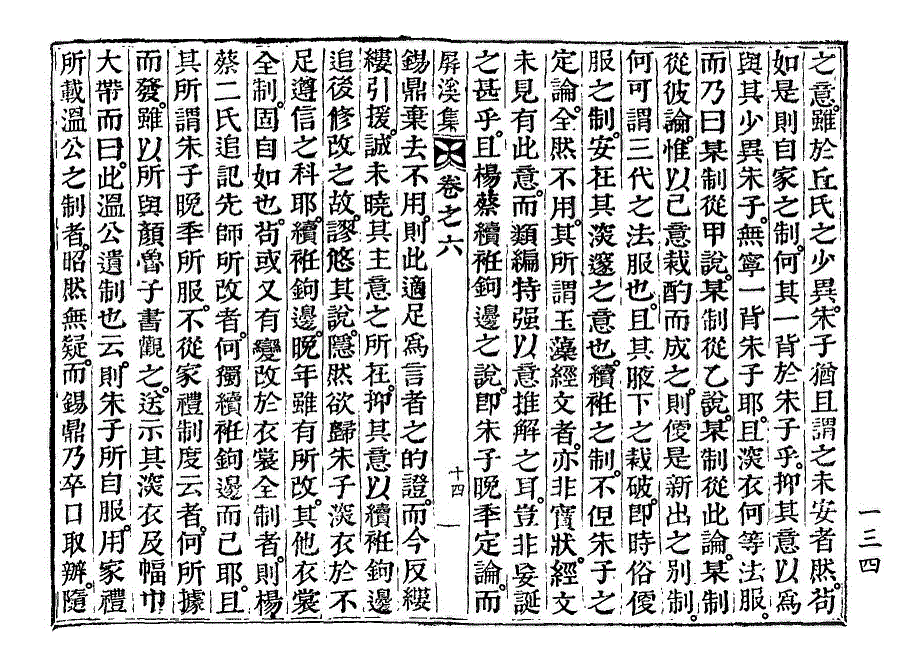 之意。虽于丘氏之少异。朱子犹且谓之未安者然。苟如是则自家之制。何其一背于朱子乎。抑其意以为与其少异朱子。无宁一背朱子耶。且深衣何等法服。而乃曰某制从甲说。某制从乙说。某制从此论。某制从彼论。惟以己意裁酌而成之。则便是新出之别制。何可谓三代之法服也。且其腋下之裁破。即时俗便服之制。安在其深邃之意也。续衽之制。不但朱子之定论。全然不用。其所谓玉藻经文者。亦非实状。经文未见有此意。而类编特强以意推解之耳。岂非妄诞之甚乎。且杨,蔡续衽钩边之说。即朱子晚年定论。而锡鼎弃去不用。则此适足为言者之的證。而今反缕缕引援。诚未晓其主意之所在。抑其意以续衽钩边追后修改之故。谬悠其说。隐然欲归朱子深衣于不足遵信之科耶。续衽钩边。晚年虽有所改。其他衣裳全制。固自如也。苟或又有变改于衣裳全制者。则杨,蔡二氏追记先师所改者。何独续衽钩边而已耶。且其所谓朱子晚年所服。不从家礼制度云者。何所据而发。虽以所与颜鲁子书观之。送示其深衣及幅巾大带而曰。此温公遗制也云。则朱子所自服。用家礼所载温公之制者。昭然无疑。而锡鼎乃卒口取办。随
之意。虽于丘氏之少异。朱子犹且谓之未安者然。苟如是则自家之制。何其一背于朱子乎。抑其意以为与其少异朱子。无宁一背朱子耶。且深衣何等法服。而乃曰某制从甲说。某制从乙说。某制从此论。某制从彼论。惟以己意裁酌而成之。则便是新出之别制。何可谓三代之法服也。且其腋下之裁破。即时俗便服之制。安在其深邃之意也。续衽之制。不但朱子之定论。全然不用。其所谓玉藻经文者。亦非实状。经文未见有此意。而类编特强以意推解之耳。岂非妄诞之甚乎。且杨,蔡续衽钩边之说。即朱子晚年定论。而锡鼎弃去不用。则此适足为言者之的證。而今反缕缕引援。诚未晓其主意之所在。抑其意以续衽钩边追后修改之故。谬悠其说。隐然欲归朱子深衣于不足遵信之科耶。续衽钩边。晚年虽有所改。其他衣裳全制。固自如也。苟或又有变改于衣裳全制者。则杨,蔡二氏追记先师所改者。何独续衽钩边而已耶。且其所谓朱子晚年所服。不从家礼制度云者。何所据而发。虽以所与颜鲁子书观之。送示其深衣及幅巾大带而曰。此温公遗制也云。则朱子所自服。用家礼所载温公之制者。昭然无疑。而锡鼎乃卒口取办。随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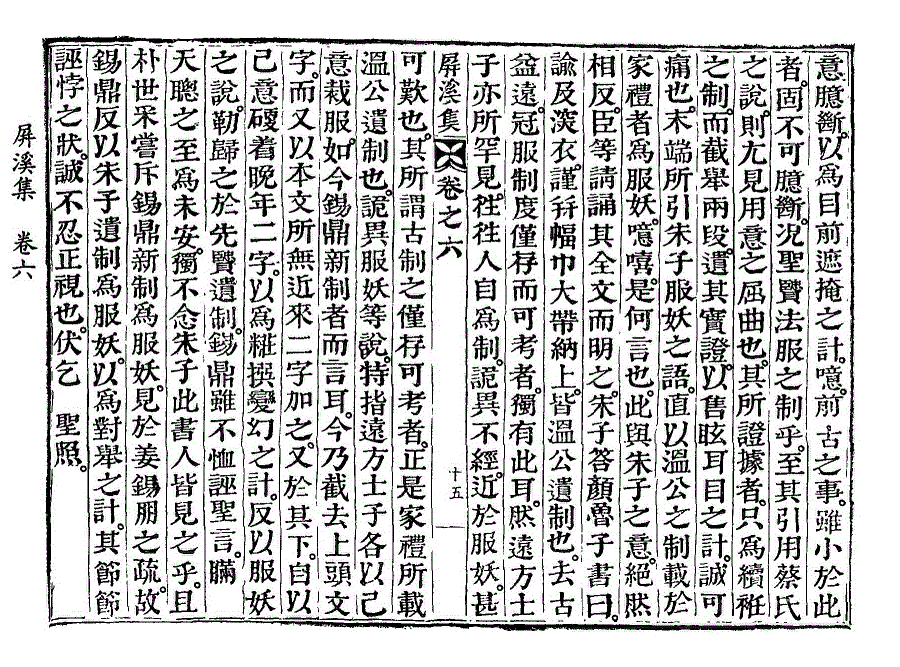 意臆断。以为目前遮掩之计。噫。前古之事。虽小于此者。固不可臆断。况圣贤法服之制乎。至其引用蔡氏之说。则尤见用意之屈曲也。其所證据者。只为续衽之制。而截举两段。遗其实證。以售眩耳目之计。诚可痛也。末端所引朱子服妖之语。直以温公之制载于家礼者为服妖。噫嘻。是何言也。此与朱子之意。绝然相反。臣等请诵其全文而明之。朱子答颜鲁子书曰。谕及深衣。谨并幅巾大带纳上。皆温公遗制也。去古益远。冠服制度仅存而可考者。独有此耳。然远方士子亦所罕见。往往人自为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其所谓古制之仅存可考者。正是家礼所载温公遗制也。诡异服妖等说。特指远方士子各以己意裁服。如今锡鼎新制者而言耳。今乃截去上头文字。而又以本文所无近来二字加之。又于其下。自以己意硬着晚年二字。以为妆撰变幻之计。反以服妖之说。勒归之于先贤遗制。锡鼎虽不恤诬圣言。瞒 天聪之至为未安。独不念朱子此书人皆见之乎。且朴世采尝斥锡鼎新制为服妖。见于姜锡朋之疏。故锡鼎反以朱子遗制为服妖。以为对举之计。其节节诬悖之状。诚不忍正视也。伏乞 圣照。
意臆断。以为目前遮掩之计。噫。前古之事。虽小于此者。固不可臆断。况圣贤法服之制乎。至其引用蔡氏之说。则尤见用意之屈曲也。其所證据者。只为续衽之制。而截举两段。遗其实證。以售眩耳目之计。诚可痛也。末端所引朱子服妖之语。直以温公之制载于家礼者为服妖。噫嘻。是何言也。此与朱子之意。绝然相反。臣等请诵其全文而明之。朱子答颜鲁子书曰。谕及深衣。谨并幅巾大带纳上。皆温公遗制也。去古益远。冠服制度仅存而可考者。独有此耳。然远方士子亦所罕见。往往人自为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其所谓古制之仅存可考者。正是家礼所载温公遗制也。诡异服妖等说。特指远方士子各以己意裁服。如今锡鼎新制者而言耳。今乃截去上头文字。而又以本文所无近来二字加之。又于其下。自以己意硬着晚年二字。以为妆撰变幻之计。反以服妖之说。勒归之于先贤遗制。锡鼎虽不恤诬圣言。瞒 天聪之至为未安。独不念朱子此书人皆见之乎。且朴世采尝斥锡鼎新制为服妖。见于姜锡朋之疏。故锡鼎反以朱子遗制为服妖。以为对举之计。其节节诬悖之状。诚不忍正视也。伏乞 圣照。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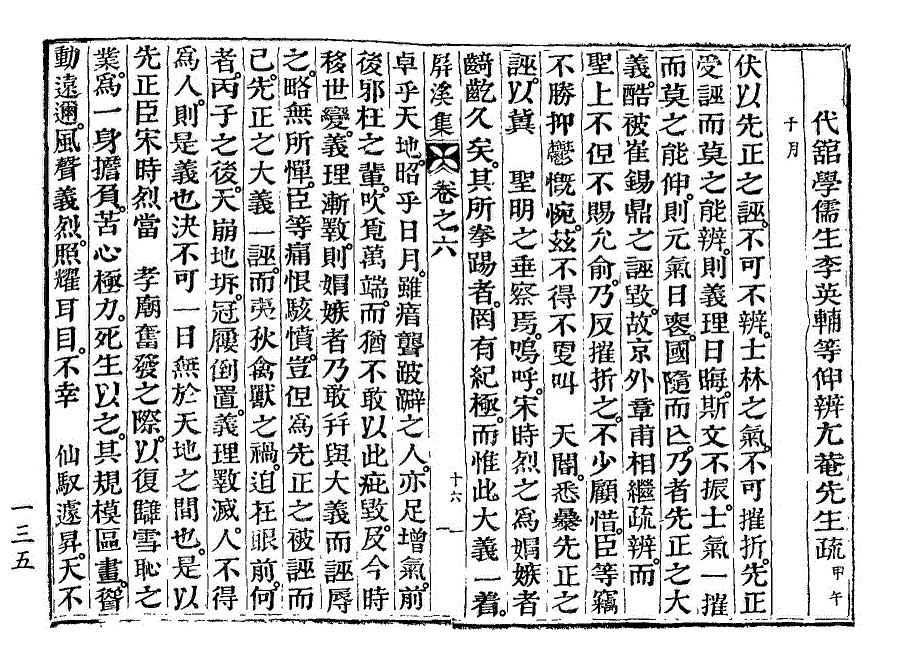 代馆学儒生李英辅等伸辨尤庵先生疏(甲午十月)
代馆学儒生李英辅等伸辨尤庵先生疏(甲午十月)伏以先正之诬。不可不辨。士林之气。不可摧折。先正受诬而莫之能辨。则义理日晦。斯文不振。士气一摧而莫之能伸。则元气日丧。国随而亡。乃者先正之大义。酷被崔锡鼎之诬毁。故京外章甫相继疏辨。而 圣上不但不赐允俞。乃反摧折之。不少顾惜。臣等窃不胜抑郁慨惋。兹不得不更叫 天阍。悉㬥先正之诬。以冀 圣明之垂察焉。呜呼。宋时烈之为媢嫉者齮龁久矣。其所拳踢者。罔有纪极。而惟此大义一着。卓乎天地。昭乎日月。虽瘖聋跛躄之人。亦足增气。前后邪枉之辈。吹觅万端。而犹不敢以此疵毁。及今时移世变。义理渐斁。则媢嫉者乃敢并与大义而诬辱之。略无所惮。臣等痛恨骇愤。岂但为先正之被诬而已。先正之大义一诬。而夷狄禽兽之祸。迫在眼前。何者。丙子之后。天崩地坼。冠屦倒置。义理斁灭。人不得为人。则是义也决不可一日无于天地之间也。是以先正臣宋时烈当 孝庙奋发之际。以复雠雪耻之业。为一身担负。苦心极力。死生以之。其规模区画。耸动远迩。风声义烈。照耀耳目。不幸 仙驭遽升。天不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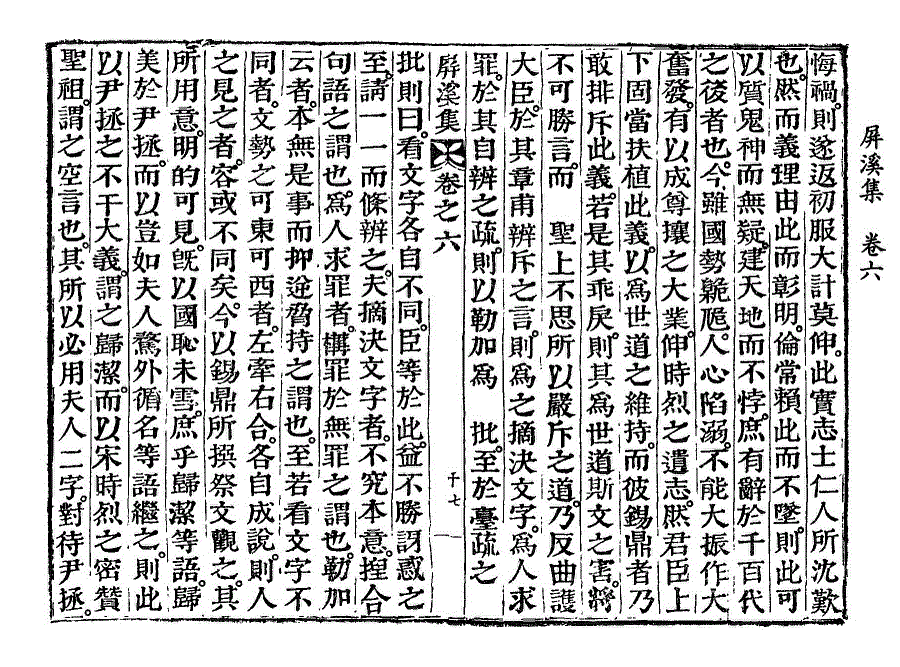 悔祸。则遂返初服大计莫伸。此实志士仁人所沈叹也。然而义理由此而彰明。伦常赖此而不坠。则此可以质鬼神而无疑。建天地而不悖。庶有辞于千百代之后者也。今虽国势臲卼。人心陷溺。不能大振作大奋发。有以成尊攘之大业。伸时烈之遗志。然君臣上下固当扶植此义。以为世道之维持。而彼锡鼎者乃敢排斥此义。若是其乖戾。则其为世道斯文之害。将不可胜言。而 圣上不思所以严斥之道。乃反曲护大臣。于其章甫辨斥之言。则为之摘决文字。为人求罪。于其自辨之疏。则以勒加为 批。至于台疏之 批则曰。看文字各自不同。臣等于此。益不胜讶惑之至。请一一而条辨之。夫摘决文字者。不究本意。捏合句语之谓也。为人求罪者。构罪于无罪之谓也。勒加云者。本无是事而抑逆胁持之谓也。至若看文字不同者。文势之可东可西者。左牵右合。各自成说。则人之见之者。容或不同矣。今以锡鼎所撰祭文观之。其所用意。明的可见。既以国耻未雪。庶乎归洁等语。归美于尹拯。而以岂如夫人骛外循名等语继之。则此以尹拯之不干大义。谓之归洁。而以宋时烈之密赞圣祖。谓之空言也。其所以必用夫人二字。对待尹拯。
悔祸。则遂返初服大计莫伸。此实志士仁人所沈叹也。然而义理由此而彰明。伦常赖此而不坠。则此可以质鬼神而无疑。建天地而不悖。庶有辞于千百代之后者也。今虽国势臲卼。人心陷溺。不能大振作大奋发。有以成尊攘之大业。伸时烈之遗志。然君臣上下固当扶植此义。以为世道之维持。而彼锡鼎者乃敢排斥此义。若是其乖戾。则其为世道斯文之害。将不可胜言。而 圣上不思所以严斥之道。乃反曲护大臣。于其章甫辨斥之言。则为之摘决文字。为人求罪。于其自辨之疏。则以勒加为 批。至于台疏之 批则曰。看文字各自不同。臣等于此。益不胜讶惑之至。请一一而条辨之。夫摘决文字者。不究本意。捏合句语之谓也。为人求罪者。构罪于无罪之谓也。勒加云者。本无是事而抑逆胁持之谓也。至若看文字不同者。文势之可东可西者。左牵右合。各自成说。则人之见之者。容或不同矣。今以锡鼎所撰祭文观之。其所用意。明的可见。既以国耻未雪。庶乎归洁等语。归美于尹拯。而以岂如夫人骛外循名等语继之。则此以尹拯之不干大义。谓之归洁。而以宋时烈之密赞圣祖。谓之空言也。其所以必用夫人二字。对待尹拯。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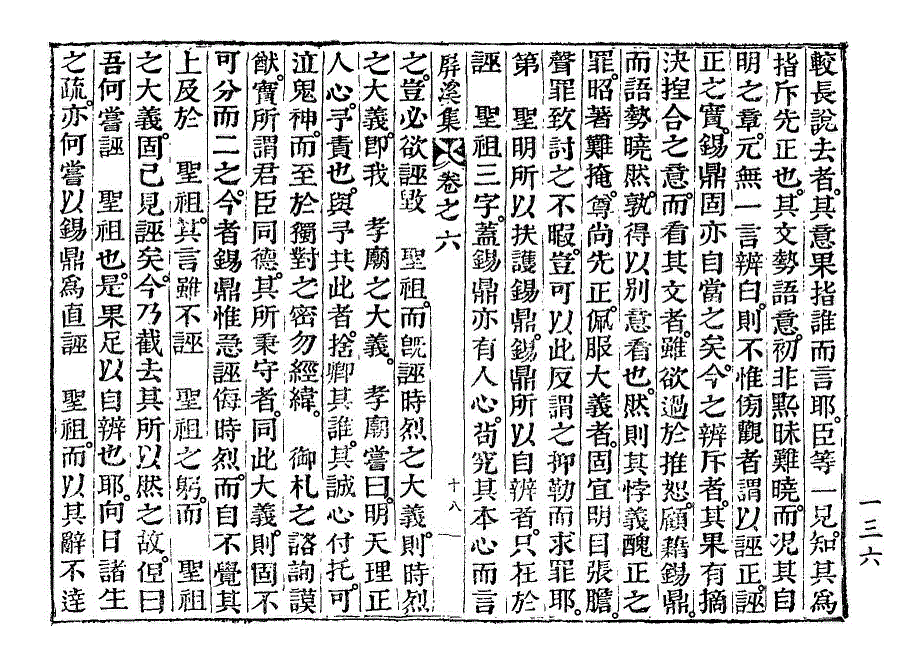 较长说去者。其意果指谁而言耶。臣等一见。知其为指斥先正也。其文势语意。初非䵝昧难晓。而况其自明之章。元无一言辨白。则不惟傍观者谓以诬正。诬正之实。锡鼎固亦自当之矣。今之辨斥者。其果有摘决捏合之意。而看其文者。虽欲过于推恕。顾藉锡鼎。而语势晓然。孰得以别意看也。然则其悖义丑正之罪。昭著难掩。尊尚先正。佩服大义者。固宜明目张胆。声罪致讨之不暇。岂可以此反谓之抑勒而求罪耶。第 圣明所以扶护锡鼎。锡鼎所以自辨者。只在于诬 圣祖三字。盖锡鼎亦有人心。苟究其本心而言之。岂必欲诬毁 圣祖。而既诬时烈之大义。则时烈之大义。即我 孝庙之大义。 孝庙尝曰。明天理正人心。予责也。与予共此者。舍卿其谁。其诚心付托。可泣鬼神。而至于独对之密勿经纬。 御札之咨询谟猷。实所谓君臣同德。其所秉守者。同此大义。则固不可分而二之。今者锡鼎惟急诬侮时烈。而自不觉其上及于 圣祖。其言虽不诬 圣祖之躬。而 圣祖之大义。固已见诬矣。今乃截去其所以然之故。但曰吾何尝诬 圣祖也。是果足以自辨也耶。向日诸生之疏。亦何尝以锡鼎为直诬 圣祖。而以其辞不达
较长说去者。其意果指谁而言耶。臣等一见。知其为指斥先正也。其文势语意。初非䵝昧难晓。而况其自明之章。元无一言辨白。则不惟傍观者谓以诬正。诬正之实。锡鼎固亦自当之矣。今之辨斥者。其果有摘决捏合之意。而看其文者。虽欲过于推恕。顾藉锡鼎。而语势晓然。孰得以别意看也。然则其悖义丑正之罪。昭著难掩。尊尚先正。佩服大义者。固宜明目张胆。声罪致讨之不暇。岂可以此反谓之抑勒而求罪耶。第 圣明所以扶护锡鼎。锡鼎所以自辨者。只在于诬 圣祖三字。盖锡鼎亦有人心。苟究其本心而言之。岂必欲诬毁 圣祖。而既诬时烈之大义。则时烈之大义。即我 孝庙之大义。 孝庙尝曰。明天理正人心。予责也。与予共此者。舍卿其谁。其诚心付托。可泣鬼神。而至于独对之密勿经纬。 御札之咨询谟猷。实所谓君臣同德。其所秉守者。同此大义。则固不可分而二之。今者锡鼎惟急诬侮时烈。而自不觉其上及于 圣祖。其言虽不诬 圣祖之躬。而 圣祖之大义。固已见诬矣。今乃截去其所以然之故。但曰吾何尝诬 圣祖也。是果足以自辨也耶。向日诸生之疏。亦何尝以锡鼎为直诬 圣祖。而以其辞不达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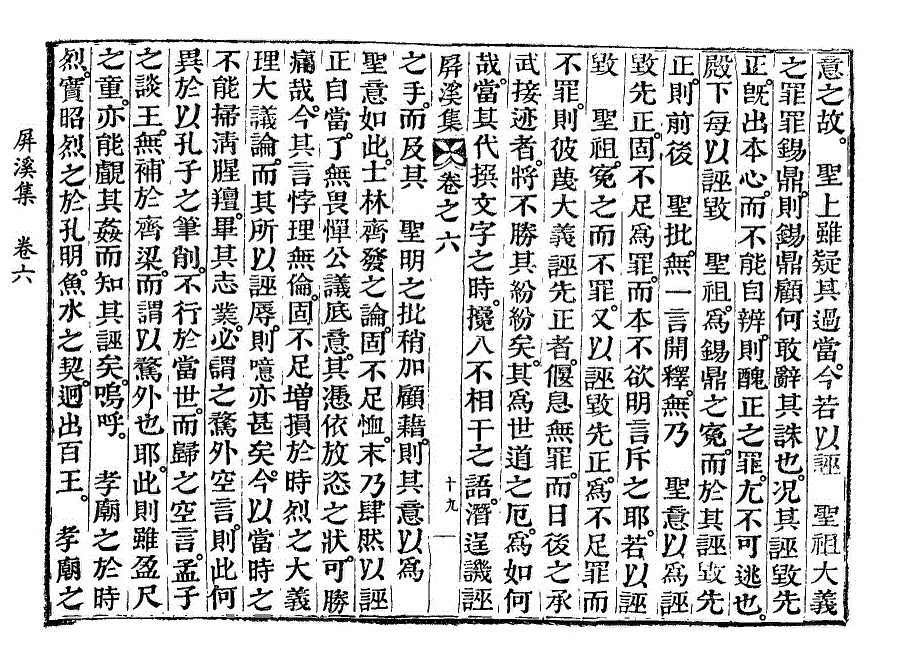 意之故。 圣上虽疑其过当。今若以诬 圣祖大义之罪罪锡鼎。则锡鼎顾何敢辞其诛也。况其诬毁先正。既出本心。而不能自辨。则丑正之罪。尤不可逃也。殿下每以诬毁 圣祖。为锡鼎之冤。而于其诬毁先正。则前后 圣批。无一言开释。无乃 圣意以为诬毁先正。固不足为罪。而本不欲明言斥之耶。若以诬毁 圣祖。冤之而不罪。又以诬毁先正。为不足罪而不罪。则彼蔑大义诬先正者。偃息无罪。而日后之承武接迹者。将不胜其纷纷矣。其为世道之厄。为如何哉。当其代撰文字之时。搀入不相干之语。潜逞讥诬之手。而及其 圣明之批稍加顾藉。则其意以为 圣意如此。士林齐发之论。固不足恤。末乃肆然以诬正自当。了无畏惮公议底意。其凭依放恣之状。可胜痛哉。今其言悖理无伦。固不足增损于时烈之大义理大议论。而其所以诬辱。则噫亦甚矣。今以当时之不能扫清腥膻。毕其志业。必谓之骛外空言。则此何异于以孔子之笔削。不行于当世。而归之空言。孟子之谈王。无补于齐梁。而谓以骛外也耶。此则虽盈尺之童。亦能觑其奸而知其诬矣。呜呼。 孝庙之于时烈。实昭烈之于孔明。鱼水之契。迥出百王。 孝庙之
意之故。 圣上虽疑其过当。今若以诬 圣祖大义之罪罪锡鼎。则锡鼎顾何敢辞其诛也。况其诬毁先正。既出本心。而不能自辨。则丑正之罪。尤不可逃也。殿下每以诬毁 圣祖。为锡鼎之冤。而于其诬毁先正。则前后 圣批。无一言开释。无乃 圣意以为诬毁先正。固不足为罪。而本不欲明言斥之耶。若以诬毁 圣祖。冤之而不罪。又以诬毁先正。为不足罪而不罪。则彼蔑大义诬先正者。偃息无罪。而日后之承武接迹者。将不胜其纷纷矣。其为世道之厄。为如何哉。当其代撰文字之时。搀入不相干之语。潜逞讥诬之手。而及其 圣明之批稍加顾藉。则其意以为 圣意如此。士林齐发之论。固不足恤。末乃肆然以诬正自当。了无畏惮公议底意。其凭依放恣之状。可胜痛哉。今其言悖理无伦。固不足增损于时烈之大义理大议论。而其所以诬辱。则噫亦甚矣。今以当时之不能扫清腥膻。毕其志业。必谓之骛外空言。则此何异于以孔子之笔削。不行于当世。而归之空言。孟子之谈王。无补于齐梁。而谓以骛外也耶。此则虽盈尺之童。亦能觑其奸而知其诬矣。呜呼。 孝庙之于时烈。实昭烈之于孔明。鱼水之契。迥出百王。 孝庙之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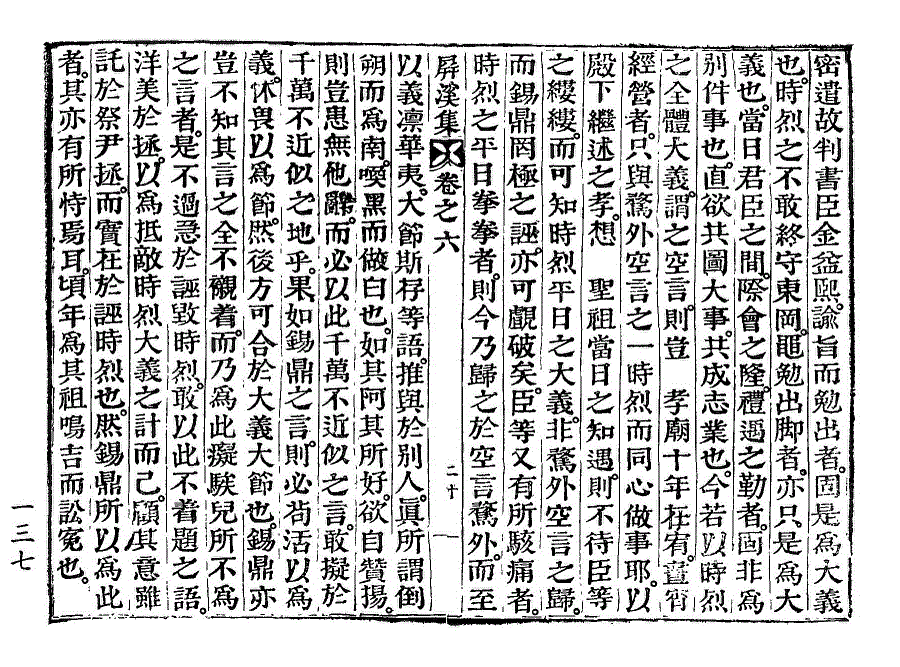 密遣故判书臣金益熙。谕旨而勉出者。固是为大义也。时烈之不敢终守东冈。黾勉出脚者。亦只是为大义也。当日君臣之间。际会之隆。礼遇之勤者。固非为别件事也。直欲共图大事。共成志业也。今若以时烈之全体大义。谓之空言。则岂 孝庙十年在宥。昼宵经营者。只与骛外空言之一时烈而同心做事耶。以殿下继述之孝。想 圣祖当日之知遇。则不待臣等之缕缕。而可知时烈平日之大义。非骛外空言之归。而锡鼎罔极之诬。亦可觑破矣。臣等又有所骇痛者。时烈之平日拳拳者。则今乃归之于空言骛外。而至以义凛华夷。大节斯存等语。推与于别人。真所谓倒朔而为南。唤黑而做白也。如其阿其所好。欲自赞扬。则岂患无他辞。而必以此千万不近似之言。敢拟于千万不近似之地乎。果如锡鼎之言。则必苟活以为义。怵畏以为节。然后方可合于大义大节也。锡鼎亦岂不知其言之全不衬着。而乃为此痴騃儿所不为之言者。是不过急于诬毁时烈。敢以此不着题之语。洋美于拯。以为抵敌时烈大义之计而已。顾其意虽托于祭尹拯。而实在于诬时烈也。然锡鼎所以为此者。其亦有所恃焉耳。顷年为其祖鸣吉而讼冤也。
密遣故判书臣金益熙。谕旨而勉出者。固是为大义也。时烈之不敢终守东冈。黾勉出脚者。亦只是为大义也。当日君臣之间。际会之隆。礼遇之勤者。固非为别件事也。直欲共图大事。共成志业也。今若以时烈之全体大义。谓之空言。则岂 孝庙十年在宥。昼宵经营者。只与骛外空言之一时烈而同心做事耶。以殿下继述之孝。想 圣祖当日之知遇。则不待臣等之缕缕。而可知时烈平日之大义。非骛外空言之归。而锡鼎罔极之诬。亦可觑破矣。臣等又有所骇痛者。时烈之平日拳拳者。则今乃归之于空言骛外。而至以义凛华夷。大节斯存等语。推与于别人。真所谓倒朔而为南。唤黑而做白也。如其阿其所好。欲自赞扬。则岂患无他辞。而必以此千万不近似之言。敢拟于千万不近似之地乎。果如锡鼎之言。则必苟活以为义。怵畏以为节。然后方可合于大义大节也。锡鼎亦岂不知其言之全不衬着。而乃为此痴騃儿所不为之言者。是不过急于诬毁时烈。敢以此不着题之语。洋美于拯。以为抵敌时烈大义之计而已。顾其意虽托于祭尹拯。而实在于诬时烈也。然锡鼎所以为此者。其亦有所恃焉耳。顷年为其祖鸣吉而讼冤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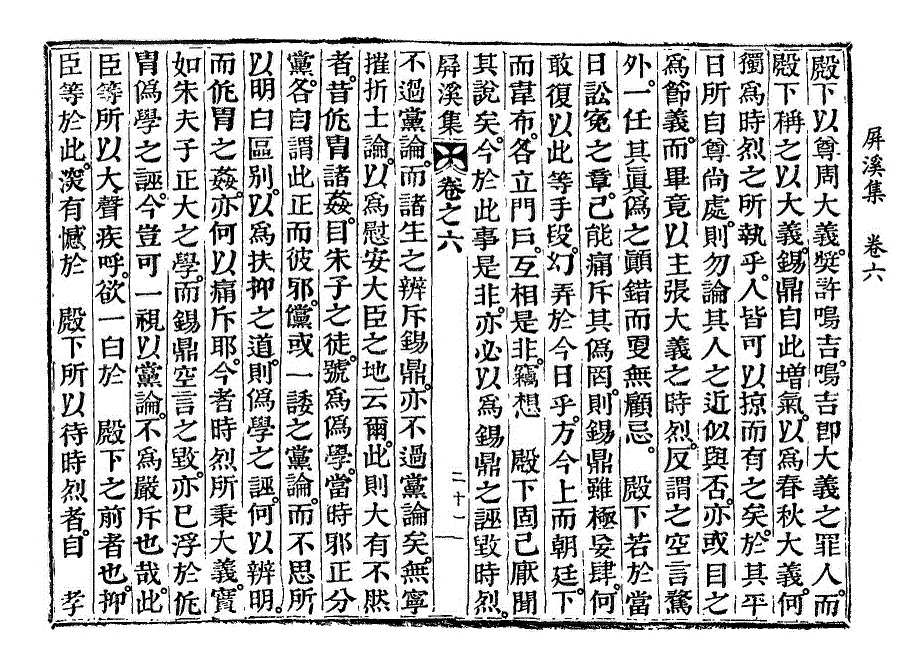 殿下以尊周大义。奖许鸣吉。鸣吉即大义之罪人。而殿下称之以大义。锡鼎自此增气。以为春秋大义。何独为时烈之所执乎。人皆可以掠而有之矣。于其平日所自尊尚处。则勿论其人之近似与否。亦或目之为节义。而毕竟以主张大义之时烈。反谓之空言骛外。一任其真伪之颠错而更无顾忌。 殿下若于当日讼冤之章。已能痛斥其伪罔。则锡鼎虽极妄肆。何敢复以此等手段。幻弄于今日乎。方今上而朝廷。下而韦布。各立门户。互相是非。窃想 殿下固已厌闻其说矣。今于此事是非。亦必以为锡鼎之诬毁时烈。不过党论。而诸生之辨斥锡鼎。亦不过党论矣。无宁摧折士论。以为慰安大臣之地云尔。此则大有不然者。昔侂胄诸奸。目朱子之徒。号为伪学。当时邪正分党。各自谓此正而彼邪。傥或一诿之党论。而不思所以明白区别。以为扶抑之道。则伪学之诬。何以辨明。而侂胄之奸。亦何以痛斥耶。今者时烈所秉大义。实如朱夫子正大之学。而锡鼎空言之毁。亦已浮于侂胄伪学之诬。今岂可一视以党论。不为严斥也哉。此臣等所以大声疾呼。欲一白于 殿下之前者也。抑臣等于此。深有憾于 殿下所以待时烈者。自 孝
殿下以尊周大义。奖许鸣吉。鸣吉即大义之罪人。而殿下称之以大义。锡鼎自此增气。以为春秋大义。何独为时烈之所执乎。人皆可以掠而有之矣。于其平日所自尊尚处。则勿论其人之近似与否。亦或目之为节义。而毕竟以主张大义之时烈。反谓之空言骛外。一任其真伪之颠错而更无顾忌。 殿下若于当日讼冤之章。已能痛斥其伪罔。则锡鼎虽极妄肆。何敢复以此等手段。幻弄于今日乎。方今上而朝廷。下而韦布。各立门户。互相是非。窃想 殿下固已厌闻其说矣。今于此事是非。亦必以为锡鼎之诬毁时烈。不过党论。而诸生之辨斥锡鼎。亦不过党论矣。无宁摧折士论。以为慰安大臣之地云尔。此则大有不然者。昔侂胄诸奸。目朱子之徒。号为伪学。当时邪正分党。各自谓此正而彼邪。傥或一诿之党论。而不思所以明白区别。以为扶抑之道。则伪学之诬。何以辨明。而侂胄之奸。亦何以痛斥耶。今者时烈所秉大义。实如朱夫子正大之学。而锡鼎空言之毁。亦已浮于侂胄伪学之诬。今岂可一视以党论。不为严斥也哉。此臣等所以大声疾呼。欲一白于 殿下之前者也。抑臣等于此。深有憾于 殿下所以待时烈者。自 孝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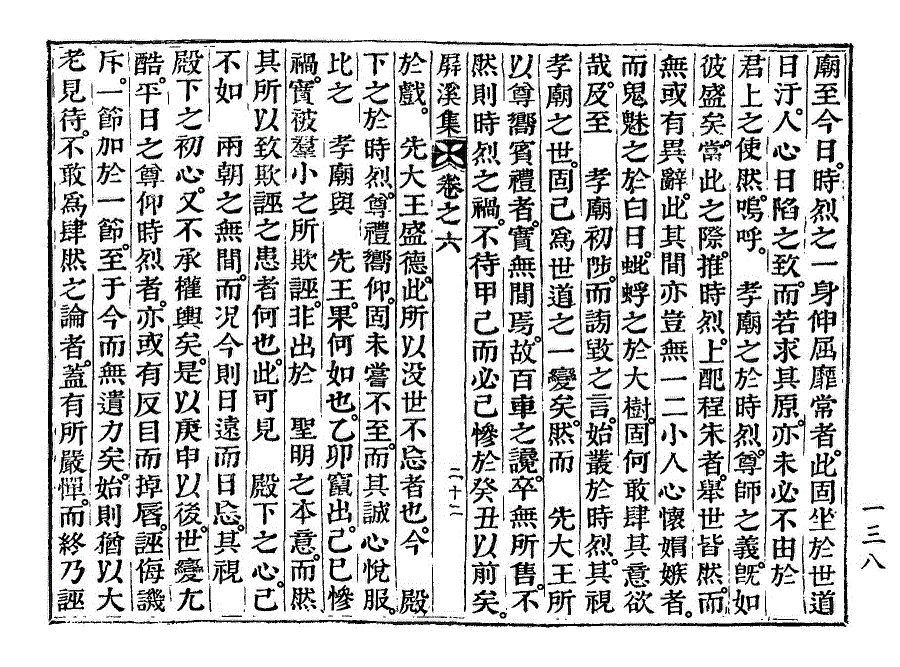 庙至今日。时烈之一身伸屈靡常者。此固坐于世道日污。人心日陷之致。而若求其原。亦未必不由于 君上之使然。呜呼。 孝庙之于时烈。尊师之义。既如彼盛矣。当此之际。推时烈。上配程朱者。举世皆然。而无或有异辞。此其间亦岂无一二小人心怀媢嫉者。而鬼魅之于白日。蚍蜉之于大树。固何敢肆其意欲哉。及至 孝庙初陟。而谤毁之言。始丛于时烈。其视孝庙之世。固已为世道之一变矣。然而 先大王所以尊向宾礼者。实无间焉。故百车之谗。卒无所售。不然则时烈之祸。不待甲己而必已惨于癸丑以前矣。于戏。 先大王盛德。此所以没世不忘者也。今 殿下之于时烈。尊礼向仰。固未尝不至。而其诚心悦服。比之 孝庙与 先王。果何如也。乙卯窜出。己巳惨祸。实被群小之所欺诬。非出于 圣明之本意。而然其所以致欺诬之患者何也。此可见 殿下之心。已不如 两朝之无间。而况今则日远而日忘。其视 殿下之初心。又不承权舆矣。是以庚申以后。世变尤酷。平日之尊仰时烈者。亦或有反目而掉唇。诬侮讥斥。一节加于一节。至于今而无遗力矣。始则犹以大老见待。不敢为肆然之论者。盖有所严惮。而终乃诬
庙至今日。时烈之一身伸屈靡常者。此固坐于世道日污。人心日陷之致。而若求其原。亦未必不由于 君上之使然。呜呼。 孝庙之于时烈。尊师之义。既如彼盛矣。当此之际。推时烈。上配程朱者。举世皆然。而无或有异辞。此其间亦岂无一二小人心怀媢嫉者。而鬼魅之于白日。蚍蜉之于大树。固何敢肆其意欲哉。及至 孝庙初陟。而谤毁之言。始丛于时烈。其视孝庙之世。固已为世道之一变矣。然而 先大王所以尊向宾礼者。实无间焉。故百车之谗。卒无所售。不然则时烈之祸。不待甲己而必已惨于癸丑以前矣。于戏。 先大王盛德。此所以没世不忘者也。今 殿下之于时烈。尊礼向仰。固未尝不至。而其诚心悦服。比之 孝庙与 先王。果何如也。乙卯窜出。己巳惨祸。实被群小之所欺诬。非出于 圣明之本意。而然其所以致欺诬之患者何也。此可见 殿下之心。已不如 两朝之无间。而况今则日远而日忘。其视 殿下之初心。又不承权舆矣。是以庚申以后。世变尤酷。平日之尊仰时烈者。亦或有反目而掉唇。诬侮讥斥。一节加于一节。至于今而无遗力矣。始则犹以大老见待。不敢为肆然之论者。盖有所严惮。而终乃诬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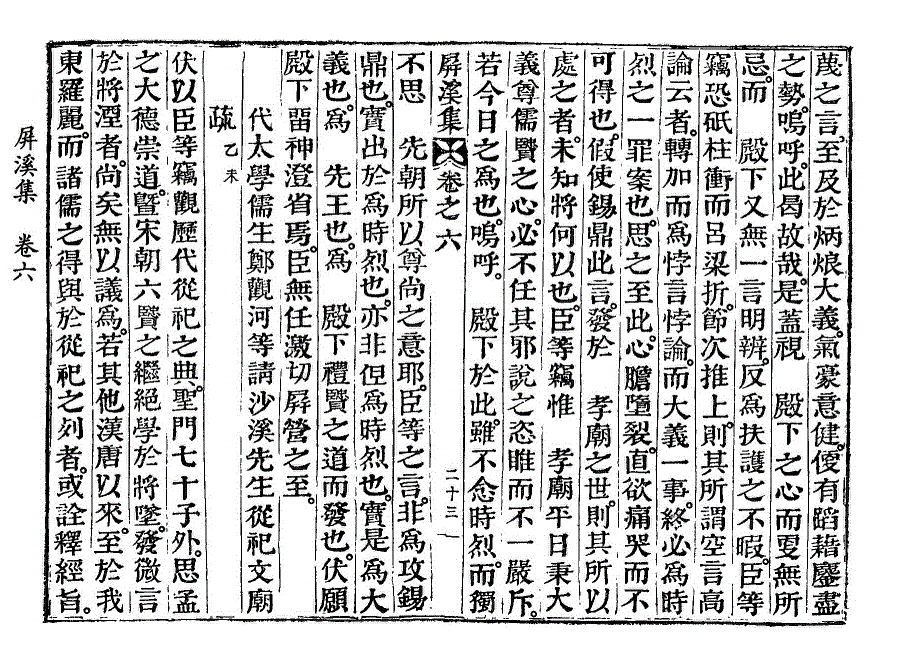 蔑之言。至及于炳烺大义。气豪意健。便有蹈藉鏖尽之势。呜呼。此曷故哉。是盖视 殿下之心而更无所忌。而 殿下又无一言明辨。反为扶护之不暇。臣等窃恐砥柱冲而吕梁折。节次推上。则其所谓空言高论云者。转加而为悖言悖论。而大义一事。终必为时烈之一罪案也。思之至此。心胆堕裂。直欲痛哭而不可得也。假使锡鼎此言。发于 孝庙之世。则其所以处之者。未知将何以也。臣等窃惟 孝庙平日秉大义尊儒贤之心。必不任其邪说之恣睢而不一严斥。若今日之为也。呜呼。 殿下于此。虽不念时烈。而独不思 先朝所以尊尚之意耶。臣等之言。非为攻锡鼎也。实出于为时烈也。亦非但为时烈也。实是为大义也。为 先王也。为 殿下礼贤之道而发也。伏愿殿下留神澄省焉。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蔑之言。至及于炳烺大义。气豪意健。便有蹈藉鏖尽之势。呜呼。此曷故哉。是盖视 殿下之心而更无所忌。而 殿下又无一言明辨。反为扶护之不暇。臣等窃恐砥柱冲而吕梁折。节次推上。则其所谓空言高论云者。转加而为悖言悖论。而大义一事。终必为时烈之一罪案也。思之至此。心胆堕裂。直欲痛哭而不可得也。假使锡鼎此言。发于 孝庙之世。则其所以处之者。未知将何以也。臣等窃惟 孝庙平日秉大义尊儒贤之心。必不任其邪说之恣睢而不一严斥。若今日之为也。呜呼。 殿下于此。虽不念时烈。而独不思 先朝所以尊尚之意耶。臣等之言。非为攻锡鼎也。实出于为时烈也。亦非但为时烈也。实是为大义也。为 先王也。为 殿下礼贤之道而发也。伏愿殿下留神澄省焉。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代太学儒生郑观河等请沙溪先生从祀文庙疏(乙未)
伏以臣等窃观历代从祀之典。圣门七十子外。思孟之大德崇道。暨宋朝六贤之继绝学于将坠。发微言于将湮者。尚矣无以议为。若其他汉唐以来。至于我东罗丽。而诸儒之得与于从祀之列者。或诠释经旨。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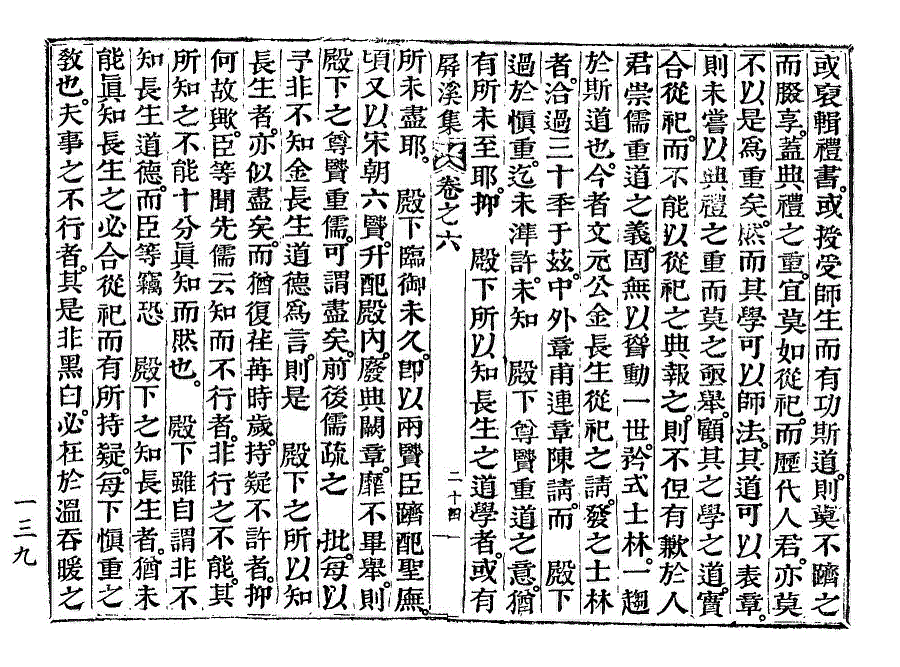 或裒辑礼书。或授受师生而有功斯道。则莫不跻之而啜享。盖典礼之重。宜莫如从祀。而历代人君。亦莫不以是为重矣。然而其学可以师法。其道可以表章。则未尝以典礼之重而莫之亟举。顾其之学之道。实合从祀。而不能以从祀之典报之。则不但有歉于人君崇儒重道之义。固无以耸动一世。矜式士林。一趋于斯道也。今者文元公金长生从祀之请。发之士林者。洽过三十年于兹。中外章甫连章陈请。而 殿下过于慎重。迄未准许。未知 殿下尊贤重道之意。犹有所未至耶。抑 殿下所以知长生之道学者。或有所未尽耶。 殿下临御未久。即以两贤臣跻配圣庑。顷又以宋朝六贤。升配殿内。废典阙章。靡不毕举。则殿下之尊贤重儒。可谓尽矣。前后儒疏之 批。每以予非不知金长生道德为言。则是 殿下之所以知长生者。亦似尽矣。而犹复荏苒时岁。持疑不许者。抑何故欤。臣等闻先儒云知而不行者。非行之不能。其所知之不能十分真知而然也。 殿下虽自谓非不知长生道德。而臣等窃恐 殿下之知长生者。犹未能真知长生之必合从祀而有所持疑。每下慎重之教也。夫事之不行者。其是非黑白。必在于温吞暖之
或裒辑礼书。或授受师生而有功斯道。则莫不跻之而啜享。盖典礼之重。宜莫如从祀。而历代人君。亦莫不以是为重矣。然而其学可以师法。其道可以表章。则未尝以典礼之重而莫之亟举。顾其之学之道。实合从祀。而不能以从祀之典报之。则不但有歉于人君崇儒重道之义。固无以耸动一世。矜式士林。一趋于斯道也。今者文元公金长生从祀之请。发之士林者。洽过三十年于兹。中外章甫连章陈请。而 殿下过于慎重。迄未准许。未知 殿下尊贤重道之意。犹有所未至耶。抑 殿下所以知长生之道学者。或有所未尽耶。 殿下临御未久。即以两贤臣跻配圣庑。顷又以宋朝六贤。升配殿内。废典阙章。靡不毕举。则殿下之尊贤重儒。可谓尽矣。前后儒疏之 批。每以予非不知金长生道德为言。则是 殿下之所以知长生者。亦似尽矣。而犹复荏苒时岁。持疑不许者。抑何故欤。臣等闻先儒云知而不行者。非行之不能。其所知之不能十分真知而然也。 殿下虽自谓非不知长生道德。而臣等窃恐 殿下之知长生者。犹未能真知长生之必合从祀而有所持疑。每下慎重之教也。夫事之不行者。其是非黑白。必在于温吞暖之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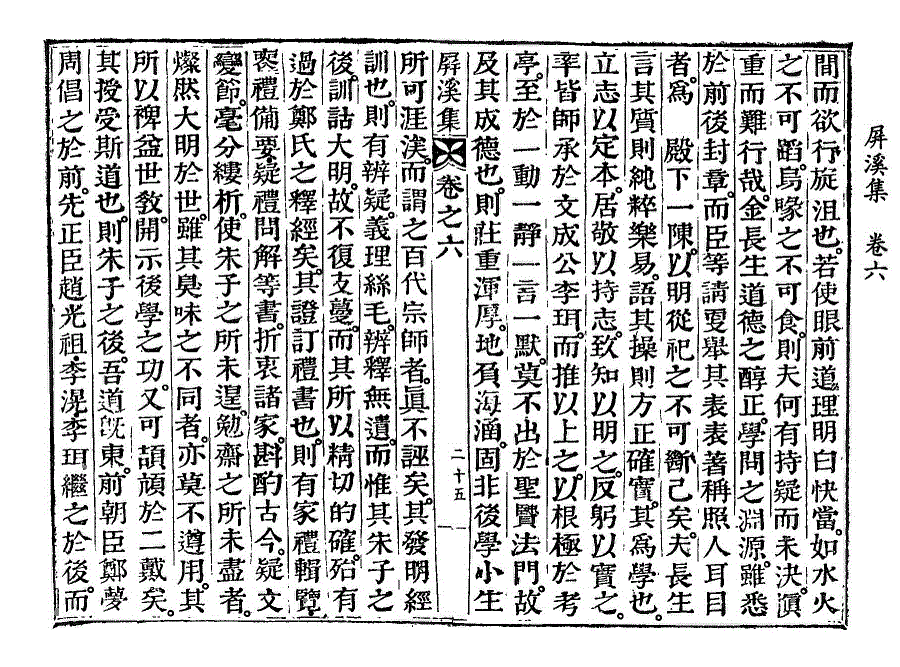 间而欲行旋沮也。若使眼前道理明白快当。如水火之不可蹈。乌喙之不可食。则夫何有持疑而未决。慎重而难行哉。金长生道德之醇正。学问之渊源。虽悉于前后封章。而臣等请更举其表表著称照人耳目者。为 殿下一陈。以明从祀之不可断已矣。夫长生言其质则纯粹乐易。语其操则方正确实。其为学也。立志以定本。居敬以持志。致知以明之。反躬以实之。率皆师承于文成公李珥。而推以上之。以根极于考亭。至于一动一静一言一默。莫不出于圣贤法门。故及其成德也。则庄重浑厚。地负海涵。固非后学小生所可涯涘。而谓之百代宗师者。真不诬矣。其发明经训也。则有辨疑。义理丝毛。辨释无遗。而惟其朱子之后。训诂大明。故不复支蔓。而其所以精切的确。殆有过于郑氏之释经矣。其證订礼书也。则有家礼辑览,丧礼备要,疑礼问解等书。折衷诸家。斟酌古今。疑文变节。毫分缕析。使朱子之所未遑。勉斋之所未尽者。灿然大明于世。虽其臭味之不同者。亦莫不遵用。其所以裨益世教。开示后学之功。又可颉颃于二戴矣。其授受斯道也。则朱子之后。吾道既东。前朝臣郑梦周倡之于前。先正臣赵光祖,李滉,李珥继之于后。而
间而欲行旋沮也。若使眼前道理明白快当。如水火之不可蹈。乌喙之不可食。则夫何有持疑而未决。慎重而难行哉。金长生道德之醇正。学问之渊源。虽悉于前后封章。而臣等请更举其表表著称照人耳目者。为 殿下一陈。以明从祀之不可断已矣。夫长生言其质则纯粹乐易。语其操则方正确实。其为学也。立志以定本。居敬以持志。致知以明之。反躬以实之。率皆师承于文成公李珥。而推以上之。以根极于考亭。至于一动一静一言一默。莫不出于圣贤法门。故及其成德也。则庄重浑厚。地负海涵。固非后学小生所可涯涘。而谓之百代宗师者。真不诬矣。其发明经训也。则有辨疑。义理丝毛。辨释无遗。而惟其朱子之后。训诂大明。故不复支蔓。而其所以精切的确。殆有过于郑氏之释经矣。其證订礼书也。则有家礼辑览,丧礼备要,疑礼问解等书。折衷诸家。斟酌古今。疑文变节。毫分缕析。使朱子之所未遑。勉斋之所未尽者。灿然大明于世。虽其臭味之不同者。亦莫不遵用。其所以裨益世教。开示后学之功。又可颉颃于二戴矣。其授受斯道也。则朱子之后。吾道既东。前朝臣郑梦周倡之于前。先正臣赵光祖,李滉,李珥继之于后。而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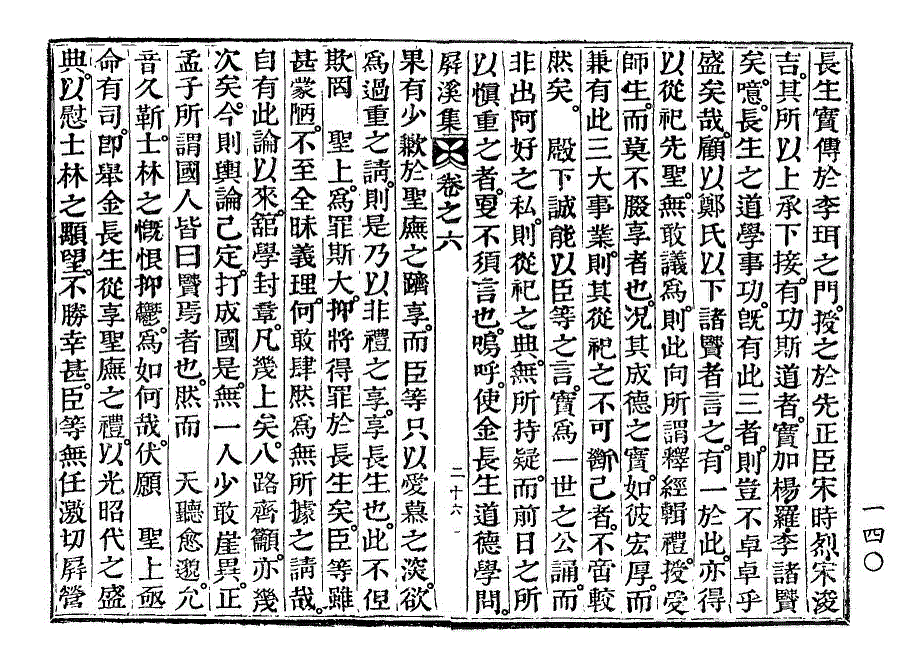 长生实传于李珥之门。授之于先正臣宋时烈,宋浚吉。其所以上承下接。有功斯道者。实加杨,罗,李诸贤矣。噫。长生之道学事功。既有此三者。则岂不卓卓乎盛矣哉。顾以郑氏以下诸贤者言之。有一于此。亦得以从祀先圣。无敢议为。则此向所谓释经辑礼。授受师生。而莫不啜享者也。况其成德之实。如彼宏厚。而兼有此三大事业。则其从祀之不可断已者。不啻较然矣。 殿下诚能以臣等之言。实为一世之公诵。而非出阿好之私。则从祀之典。无所持疑。而前日之所以慎重之者。更不须言也。呜呼。使金长生道德学问。果有少歉于圣庑之跻享。而臣等只以爱慕之深。欲为过重之请。则是乃以非礼之享。享长生也。此不但欺罔 圣上。为罪斯大。抑将得罪于长生矣。臣等虽甚蒙陋。不至全昧义理。何敢肆然为无所据之请哉。自有此论以来。馆学封章。凡几上矣。八路齐吁。亦几次矣。今则舆论已定。打成国是。无一人少敢崖异。正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焉者也。然而 天听愈邈。允音久靳。士林之慨恨抑郁。为如何哉。伏愿 圣上亟命有司。即举金长生从享圣庑之礼。以光昭代之盛典。以慰士林之颙望。不胜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
长生实传于李珥之门。授之于先正臣宋时烈,宋浚吉。其所以上承下接。有功斯道者。实加杨,罗,李诸贤矣。噫。长生之道学事功。既有此三者。则岂不卓卓乎盛矣哉。顾以郑氏以下诸贤者言之。有一于此。亦得以从祀先圣。无敢议为。则此向所谓释经辑礼。授受师生。而莫不啜享者也。况其成德之实。如彼宏厚。而兼有此三大事业。则其从祀之不可断已者。不啻较然矣。 殿下诚能以臣等之言。实为一世之公诵。而非出阿好之私。则从祀之典。无所持疑。而前日之所以慎重之者。更不须言也。呜呼。使金长生道德学问。果有少歉于圣庑之跻享。而臣等只以爱慕之深。欲为过重之请。则是乃以非礼之享。享长生也。此不但欺罔 圣上。为罪斯大。抑将得罪于长生矣。臣等虽甚蒙陋。不至全昧义理。何敢肆然为无所据之请哉。自有此论以来。馆学封章。凡几上矣。八路齐吁。亦几次矣。今则舆论已定。打成国是。无一人少敢崖异。正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焉者也。然而 天听愈邈。允音久靳。士林之慨恨抑郁。为如何哉。伏愿 圣上亟命有司。即举金长生从享圣庑之礼。以光昭代之盛典。以慰士林之颙望。不胜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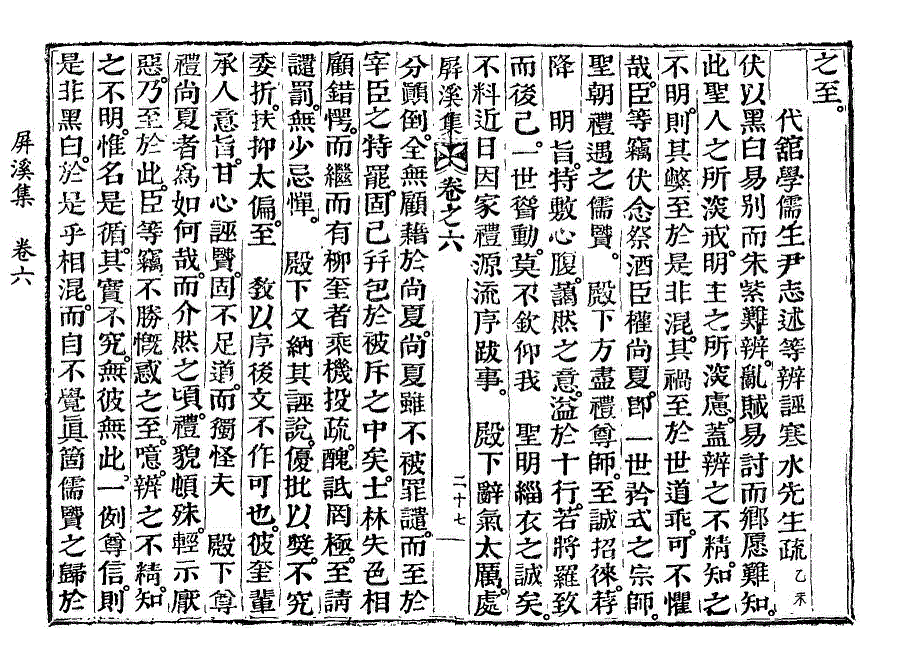 之至。
之至。代馆学儒生尹志述等辨诬寒水先生疏(乙未)
伏以黑白易别而朱紫难辨。乱贼易讨而乡愿难知。此圣人之所深戒。明主之所深虑。盖辨之不精。知之不明。则其弊至于是非混。其祸至于世道乖。可不惧哉。臣等窃伏念祭酒臣权尚夏。即一世矜式之宗师。圣朝礼遇之儒贤。 殿下方尽礼尊师。至诚招徕。荐降 明旨。特敷心腹。蔼然之意。溢于十行。若将罗致而后已。一世耸动。莫不钦仰我 圣明缁衣之诚矣。不料近日因家礼源流序跋事。 殿下辞气太厉。处分颠倒。全无顾藉于尚夏。尚夏虽不被罪谴。而至于宰臣之特罢。固已并包于被斥之中矣。士林失色相顾错愕。而继而有柳奎者乘机投疏。丑诋罔极。至请谴罚。无少忌惮。 殿下又纳其诬说。优批以奖。不究委折。扶抑太偏。至 教以序后文不作可也。彼奎辈承人意旨。甘心诬贤。固不足道。而独怪夫 殿下尊礼尚夏者为如何哉。而介然之顷。礼貌顿殊。轻示厌恶。乃至于此。臣等窃不胜慨惑之至。噫。辨之不精。知之不明。惟名是循。其实不究。无彼无此。一例尊信。则是非黑白。于是乎相混。而自不觉真个儒贤之归于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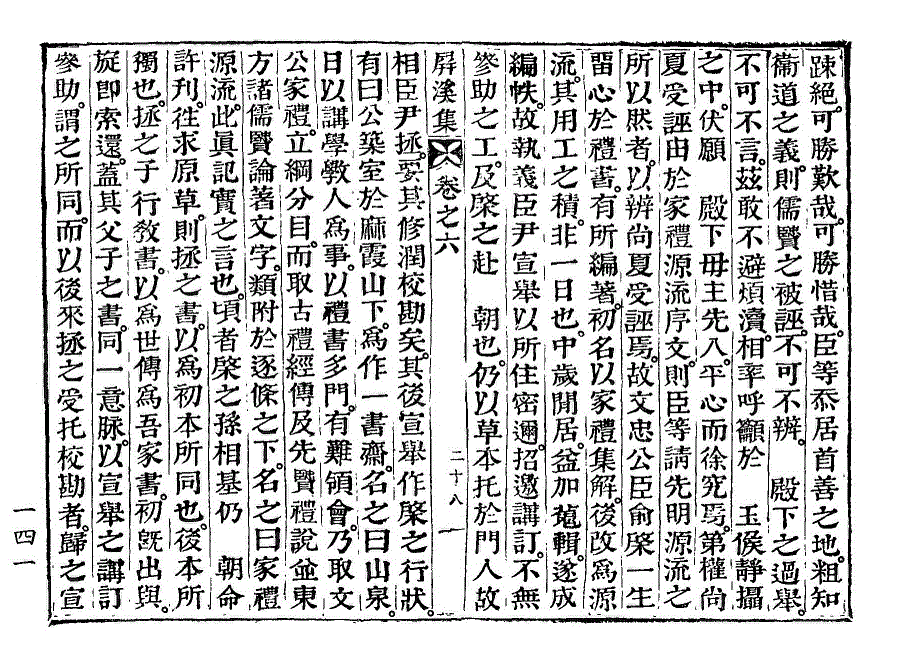 疏绝。可胜叹哉。可胜惜哉。臣等忝居首善之地。粗知卫道之义。则儒贤之被诬。不可不辨。 殿下之过举。不可不言。兹敢不避烦渎。相率呼吁于 玉候静摄之中。伏愿 殿下毋主先入。平心而徐究焉。第权尚夏受诬由于家礼源流序文。则臣等请先明源流之所以然者。以辨尚夏受诬焉。故文忠公臣俞棨一生留心于礼书。有所编著。初名以家礼集解。后改为源流。其用工之积。非一日也。中岁閒居。益加蒐辑。遂成编帙。故执义臣尹宣举以所住密迩。招邀讲订。不无参助之工。及棨之赴 朝也。仍以草本托于门人故相臣尹拯。要其修润校勘矣。其后宣举作棨之行状。有曰公筑室于麻霞山下。为作一书斋。名之曰山泉。日以讲学敩人为事。以礼书多门。有难领会。乃取文公家礼。立纲分目。而取古礼经传及先贤礼说并东方诸儒贤论著文字。类附于逐条之下。名之曰家礼源流。此真记实之言也。顷者棨之孙相基仍 朝命许刊。往求原草。则拯之书。以为初本所同也。后本所独也。拯之子行教书。以为世传为吾家书。初既出与。旋即索还。盖其父子之书。同一意脉。以宣举之讲订参助。谓之所同。而以后来拯之受托校勘者。归之宣
疏绝。可胜叹哉。可胜惜哉。臣等忝居首善之地。粗知卫道之义。则儒贤之被诬。不可不辨。 殿下之过举。不可不言。兹敢不避烦渎。相率呼吁于 玉候静摄之中。伏愿 殿下毋主先入。平心而徐究焉。第权尚夏受诬由于家礼源流序文。则臣等请先明源流之所以然者。以辨尚夏受诬焉。故文忠公臣俞棨一生留心于礼书。有所编著。初名以家礼集解。后改为源流。其用工之积。非一日也。中岁閒居。益加蒐辑。遂成编帙。故执义臣尹宣举以所住密迩。招邀讲订。不无参助之工。及棨之赴 朝也。仍以草本托于门人故相臣尹拯。要其修润校勘矣。其后宣举作棨之行状。有曰公筑室于麻霞山下。为作一书斋。名之曰山泉。日以讲学敩人为事。以礼书多门。有难领会。乃取文公家礼。立纲分目。而取古礼经传及先贤礼说并东方诸儒贤论著文字。类附于逐条之下。名之曰家礼源流。此真记实之言也。顷者棨之孙相基仍 朝命许刊。往求原草。则拯之书。以为初本所同也。后本所独也。拯之子行教书。以为世传为吾家书。初既出与。旋即索还。盖其父子之书。同一意脉。以宣举之讲订参助。谓之所同。而以后来拯之受托校勘者。归之宣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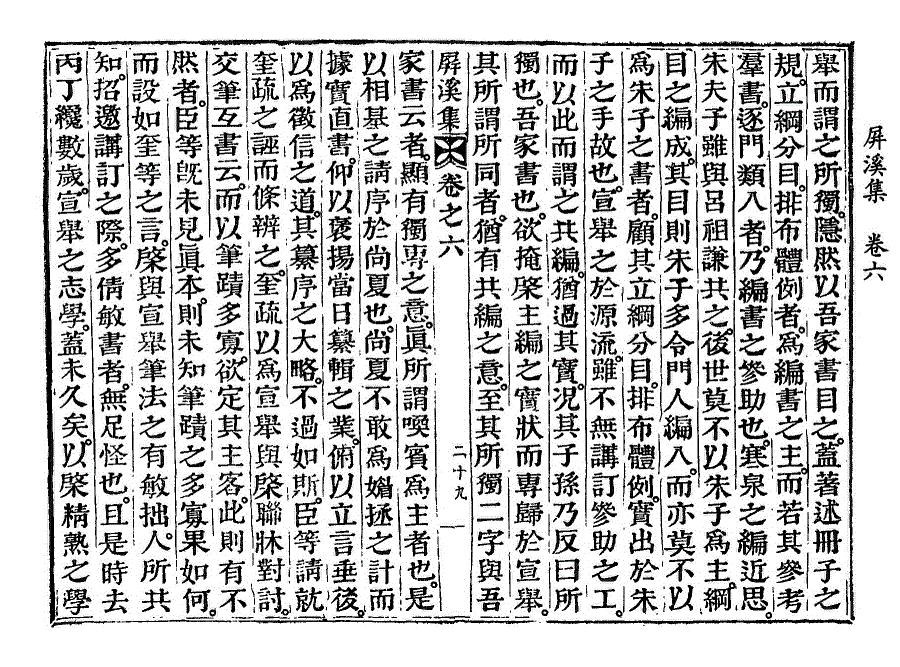 举而谓之所独。隐然以吾家书目之。盖著述册子之规。立纲分目。排布体例者。为编书之主。而若其参考群书。逐门类入者。乃编书之参助也。寒泉之编近思。朱夫子虽与吕祖谦共之。后世莫不以朱子为主。纲目之编成。其目则朱子多令门人编入。而亦莫不以为朱子之书者。顾其立纲分目。排布体例。实出于朱子之手故也。宣举之于源流。虽不无讲订参助之工。而以此而谓之共编。犹过其实。况其子孙乃反曰所独也。吾家书也。欲掩棨主编之实状而专归于宣举。其所谓所同者。犹有共编之意。至其所独二字与吾家书云者。显有独专之意。真所谓唤宾为主者也。是以相基之请序于尚夏也。尚夏不敢为媚拯之计而据实直书。仰以褒扬当日纂辑之业。俯以立言垂后。以为徵信之道。其纂序之大略。不过如斯。臣等请就奎疏之诬而条辨之。奎疏以为宣举与棨联床对讨。交笔互书云。而以笔迹多寡。欲定其主客。此则有不然者。臣等既未见真本。则未知笔迹之多寡果如何。而设如奎等之言。棨与宣举笔法之有敏拙。人所共知。招邀讲订之际。多倩敏书者。无足怪也。且是时去丙丁才数岁。宣举之志学。盖未久矣。以棨精熟之学
举而谓之所独。隐然以吾家书目之。盖著述册子之规。立纲分目。排布体例者。为编书之主。而若其参考群书。逐门类入者。乃编书之参助也。寒泉之编近思。朱夫子虽与吕祖谦共之。后世莫不以朱子为主。纲目之编成。其目则朱子多令门人编入。而亦莫不以为朱子之书者。顾其立纲分目。排布体例。实出于朱子之手故也。宣举之于源流。虽不无讲订参助之工。而以此而谓之共编。犹过其实。况其子孙乃反曰所独也。吾家书也。欲掩棨主编之实状而专归于宣举。其所谓所同者。犹有共编之意。至其所独二字与吾家书云者。显有独专之意。真所谓唤宾为主者也。是以相基之请序于尚夏也。尚夏不敢为媚拯之计而据实直书。仰以褒扬当日纂辑之业。俯以立言垂后。以为徵信之道。其纂序之大略。不过如斯。臣等请就奎疏之诬而条辨之。奎疏以为宣举与棨联床对讨。交笔互书云。而以笔迹多寡。欲定其主客。此则有不然者。臣等既未见真本。则未知笔迹之多寡果如何。而设如奎等之言。棨与宣举笔法之有敏拙。人所共知。招邀讲订之际。多倩敏书者。无足怪也。且是时去丙丁才数岁。宣举之志学。盖未久矣。以棨精熟之学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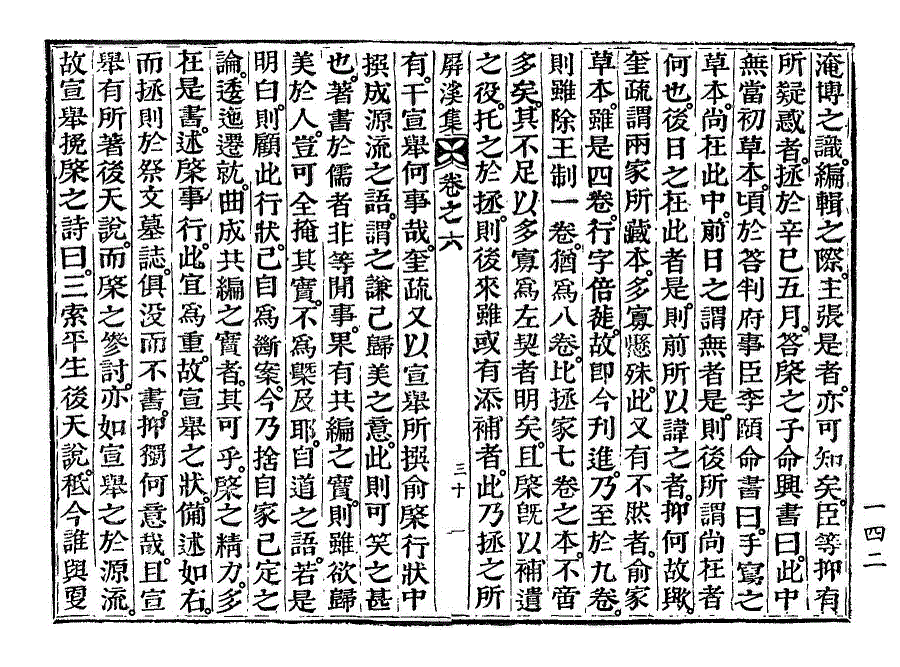 淹博之识。编辑之际。主张是者。亦可知矣。臣等抑有所疑惑者。拯于辛巳五月。答棨之子命兴书曰。此中无当初草本。顷于答判府事臣李颐命书曰。手写之草本。尚在此中。前日之谓无者是。则后所谓尚在者何也。后日之在此者是。则前所以讳之者。抑何故欤。奎疏谓两家所藏本。多寡悬殊。此又有不然者。俞家草本。虽是四卷。行字倍蓰。故即今刊进。乃至于九卷。则虽除王制一卷。犹为八卷。比拯家七卷之本。不啻多矣。其不足以多寡为左契者明矣。且棨既以补遗之役。托之于拯。则后来虽或有添补者。此乃拯之所有。干宣举何事哉。奎疏又以宣举所撰俞棨行状中撰成源流之语。谓之谦己归美之意。此则可笑之甚也。著书于儒者非等閒事。果有共编之实。则虽欲归美于人。岂可全掩其实。不为槩及耶。自道之语。若是明白。则顾此行状。已自为断案。今乃舍自家已定之论。逶迤迁就。曲成共编之实者。其可乎。棨之精力。多在是书。述棨事行。此宜为重。故宣举之状。备述如右。而拯则于祭文墓志。俱没而不书。抑独何意哉。且宣举有所著后天说。而棨之参讨。亦如宣举之于源流。故宣举挽棨之诗曰。三索平生后天说。秪今谁与更
淹博之识。编辑之际。主张是者。亦可知矣。臣等抑有所疑惑者。拯于辛巳五月。答棨之子命兴书曰。此中无当初草本。顷于答判府事臣李颐命书曰。手写之草本。尚在此中。前日之谓无者是。则后所谓尚在者何也。后日之在此者是。则前所以讳之者。抑何故欤。奎疏谓两家所藏本。多寡悬殊。此又有不然者。俞家草本。虽是四卷。行字倍蓰。故即今刊进。乃至于九卷。则虽除王制一卷。犹为八卷。比拯家七卷之本。不啻多矣。其不足以多寡为左契者明矣。且棨既以补遗之役。托之于拯。则后来虽或有添补者。此乃拯之所有。干宣举何事哉。奎疏又以宣举所撰俞棨行状中撰成源流之语。谓之谦己归美之意。此则可笑之甚也。著书于儒者非等閒事。果有共编之实。则虽欲归美于人。岂可全掩其实。不为槩及耶。自道之语。若是明白。则顾此行状。已自为断案。今乃舍自家已定之论。逶迤迁就。曲成共编之实者。其可乎。棨之精力。多在是书。述棨事行。此宜为重。故宣举之状。备述如右。而拯则于祭文墓志。俱没而不书。抑独何意哉。且宣举有所著后天说。而棨之参讨。亦如宣举之于源流。故宣举挽棨之诗曰。三索平生后天说。秪今谁与更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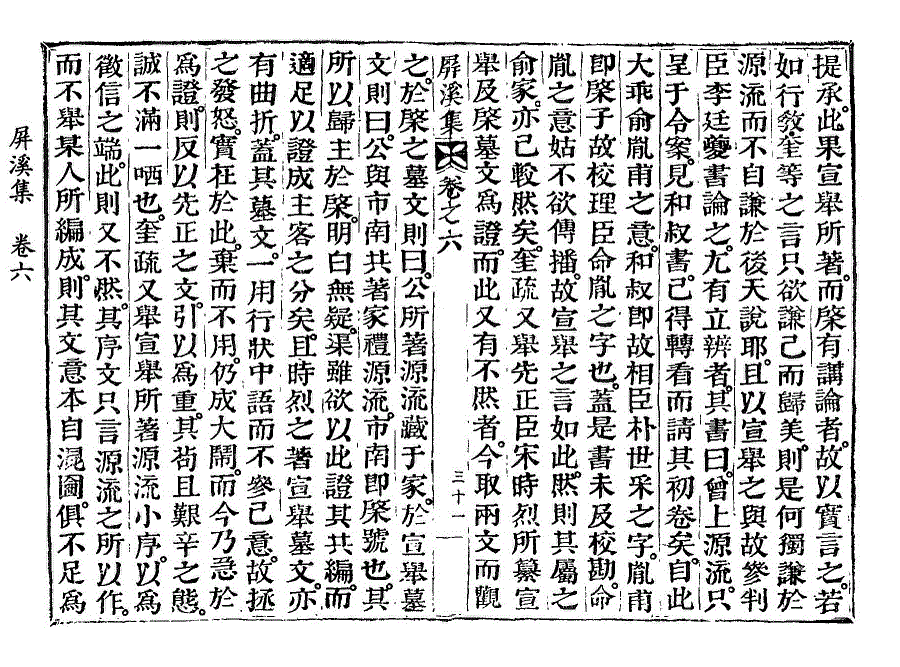 提承。此果宣举所著。而棨有讲论者。故以实言之。若如行教,奎等之言只欲谦己而归美。则是何独谦于源流而不自谦于后天说耶。且以宣举之与故参判臣李廷夔书论之。尤有立辨者。其书曰。曾上源流。只呈于令案。见和叔书。已得转看而请其初卷矣。自此大乖俞胤甫之意。和叔即故相臣朴世采之字。胤甫即棨子故校理臣命胤之字也。盖是书未及校勘。命胤之意姑不欲传播。故宣举之言如此。然则其属之俞家。亦已较然矣。奎疏又举先正臣宋时烈所纂宣举及棨墓文为證。而此又有不然者。今取两文而观之。于棨之墓文则曰。公所著源流藏于家。于宣举墓文则曰。公与市南共著家礼源流。市南即棨号也。其所以归主于棨。明白无疑。渠虽欲以此證其共编。而适足以證成主客之分矣。且时烈之著宣举墓文。亦有曲折。盖其墓文。一用行状中语而不参己意。故拯之发怒。实在于此。弃而不用。仍成大闹。而今乃急于为證。则反以先正之文。引以为重。其苟且艰辛之态。诚不满一哂也。奎疏又举宣举所著源流小序。以为徵信之端。此则又不然。其序文只言源流之所以作。而不举某人所编成。则其文意本自混囵。俱不足为
提承。此果宣举所著。而棨有讲论者。故以实言之。若如行教,奎等之言只欲谦己而归美。则是何独谦于源流而不自谦于后天说耶。且以宣举之与故参判臣李廷夔书论之。尤有立辨者。其书曰。曾上源流。只呈于令案。见和叔书。已得转看而请其初卷矣。自此大乖俞胤甫之意。和叔即故相臣朴世采之字。胤甫即棨子故校理臣命胤之字也。盖是书未及校勘。命胤之意姑不欲传播。故宣举之言如此。然则其属之俞家。亦已较然矣。奎疏又举先正臣宋时烈所纂宣举及棨墓文为證。而此又有不然者。今取两文而观之。于棨之墓文则曰。公所著源流藏于家。于宣举墓文则曰。公与市南共著家礼源流。市南即棨号也。其所以归主于棨。明白无疑。渠虽欲以此證其共编。而适足以證成主客之分矣。且时烈之著宣举墓文。亦有曲折。盖其墓文。一用行状中语而不参己意。故拯之发怒。实在于此。弃而不用。仍成大闹。而今乃急于为證。则反以先正之文。引以为重。其苟且艰辛之态。诚不满一哂也。奎疏又举宣举所著源流小序。以为徵信之端。此则又不然。其序文只言源流之所以作。而不举某人所编成。则其文意本自混囵。俱不足为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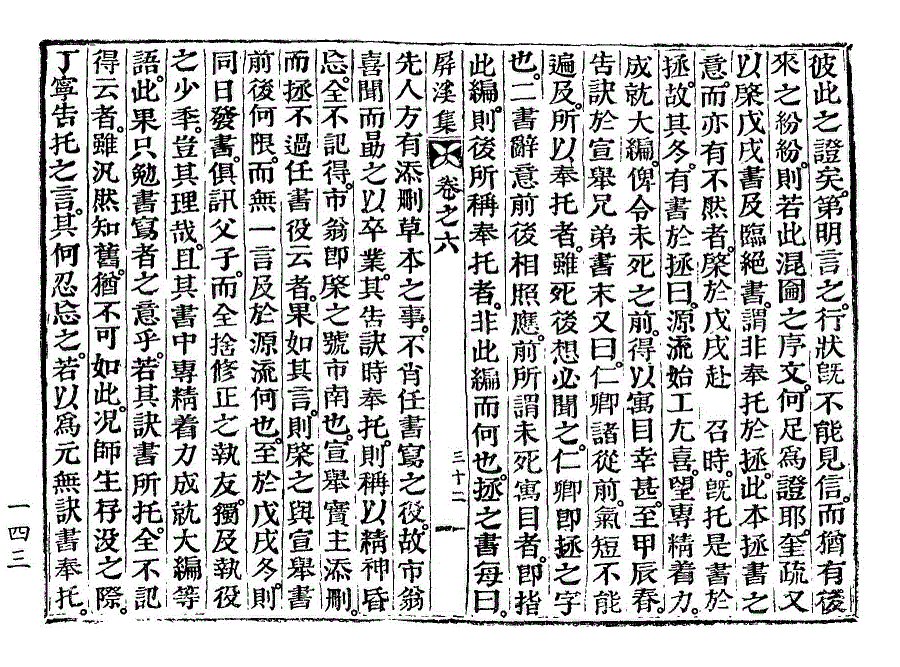 彼此之證矣。第明言之。行状既不能见信。而犹有后来之纷纷。则若此混囵之序文。何足为證耶。奎疏又以棨戊戌书及临绝书。谓非奉托于拯。此本拯书之意。而亦有不然者。棨于戊戌赴 召时。既托是书于拯。故其冬。有书于拯曰。源流始工尤喜。望专精着力。成就大编。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至甲辰春。告诀于宣举兄弟书末又曰。仁卿诸从前。气短不能遍及。所以奉托者。虽死后想必闻之。仁卿即拯之字也。二书辞意前后相照应。前所谓未死寓目者。即指此编。则后所称奉托者。非此编而何也。拯之书每曰。先人方有添删草本之事。不肖任书写之役。故市翁喜闻而勖之以卒业。其告诀时奉托。则称以精神昏忘。全不记得。市翁即棨之号市南也。宣举实主添删。而拯不过任书役云者。果如其言。则棨之与宣举书前后何限。而无一言及于源流何也。至于戊戌冬。则同日发书。俱讯父子。而全舍修正之执友。独及执役之少年。岂其理哉。且其书中专精着力成就大编等语。此果只勉书写者之意乎。若其诀书所托。全不记得云者。虽汎然知旧。犹不可如此。况师生存没之际。丁宁告托之言。其何忍忘之。若以为元无诀书奉托。
彼此之證矣。第明言之。行状既不能见信。而犹有后来之纷纷。则若此混囵之序文。何足为證耶。奎疏又以棨戊戌书及临绝书。谓非奉托于拯。此本拯书之意。而亦有不然者。棨于戊戌赴 召时。既托是书于拯。故其冬。有书于拯曰。源流始工尤喜。望专精着力。成就大编。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至甲辰春。告诀于宣举兄弟书末又曰。仁卿诸从前。气短不能遍及。所以奉托者。虽死后想必闻之。仁卿即拯之字也。二书辞意前后相照应。前所谓未死寓目者。即指此编。则后所称奉托者。非此编而何也。拯之书每曰。先人方有添删草本之事。不肖任书写之役。故市翁喜闻而勖之以卒业。其告诀时奉托。则称以精神昏忘。全不记得。市翁即棨之号市南也。宣举实主添删。而拯不过任书役云者。果如其言。则棨之与宣举书前后何限。而无一言及于源流何也。至于戊戌冬。则同日发书。俱讯父子。而全舍修正之执友。独及执役之少年。岂其理哉。且其书中专精着力成就大编等语。此果只勉书写者之意乎。若其诀书所托。全不记得云者。虽汎然知旧。犹不可如此。况师生存没之际。丁宁告托之言。其何忍忘之。若以为元无诀书奉托。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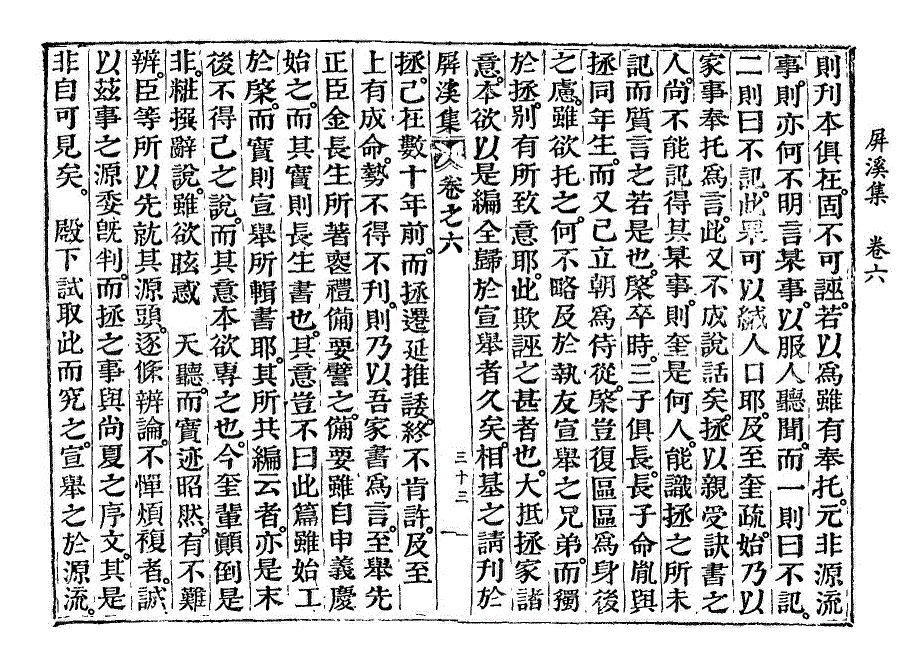 则刊本俱在。固不可诬。若以为虽有奉托。元非源流事。则亦何不明言某事。以服人听闻。而一则曰不记。二则曰不记。此果可以缄人口耶。及至奎疏。始乃以家事奉托为言。此又不成说话矣。拯以亲受诀书之人。尚不能记得其某事。则奎是何人。能识拯之所未记而质言之若是也。棨卒时。三子俱长。长子命胤与拯同年生。而又已立朝为侍从。棨岂复区区为身后之虑。虽欲托之。何不略及于执友宣举之兄弟。而独于拯。别有所致意耶。此欺诬之甚者也。大抵拯家诸意。本欲以是编全归于宣举者久矣。相基之请刊于拯。已在数十年前。而拯迁延推诿。终不肯许。及至 上有成命。势不得不刊。则乃以吾家书为言。至举先正臣金长生所著丧礼备要譬之。备要虽自申义庆始之。而其实则长生书也。其意岂不曰此篇虽始工于棨。而实则宣举所辑书耶。其所共编云者。亦是末后不得已之说。而其意本欲专之也。今奎辈颠倒是非。妆撰辞说。虽欲眩惑 天听。而实迹昭然。有不难辨。臣等所以先就其源头。逐条辨论。不惮烦复者。诚以兹事之源委既判。而拯之事与尚夏之序文。其是非自可见矣。 殿下试取此而究之。宣举之于源流。
则刊本俱在。固不可诬。若以为虽有奉托。元非源流事。则亦何不明言某事。以服人听闻。而一则曰不记。二则曰不记。此果可以缄人口耶。及至奎疏。始乃以家事奉托为言。此又不成说话矣。拯以亲受诀书之人。尚不能记得其某事。则奎是何人。能识拯之所未记而质言之若是也。棨卒时。三子俱长。长子命胤与拯同年生。而又已立朝为侍从。棨岂复区区为身后之虑。虽欲托之。何不略及于执友宣举之兄弟。而独于拯。别有所致意耶。此欺诬之甚者也。大抵拯家诸意。本欲以是编全归于宣举者久矣。相基之请刊于拯。已在数十年前。而拯迁延推诿。终不肯许。及至 上有成命。势不得不刊。则乃以吾家书为言。至举先正臣金长生所著丧礼备要譬之。备要虽自申义庆始之。而其实则长生书也。其意岂不曰此篇虽始工于棨。而实则宣举所辑书耶。其所共编云者。亦是末后不得已之说。而其意本欲专之也。今奎辈颠倒是非。妆撰辞说。虽欲眩惑 天听。而实迹昭然。有不难辨。臣等所以先就其源头。逐条辨论。不惮烦复者。诚以兹事之源委既判。而拯之事与尚夏之序文。其是非自可见矣。 殿下试取此而究之。宣举之于源流。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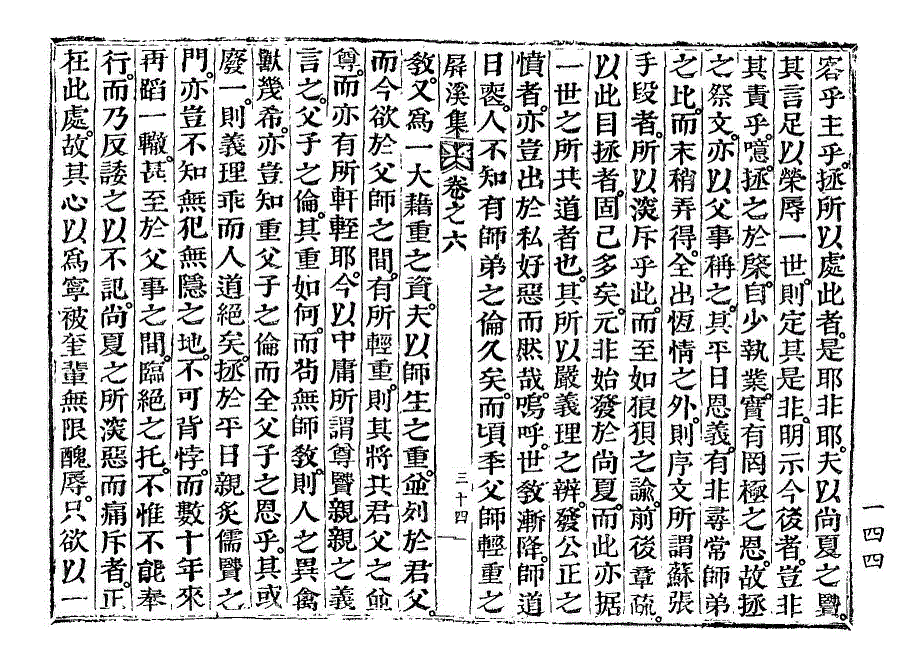 客乎主乎。拯所以处此者。是耶非耶。夫以尚夏之贤。其言足以荣辱一世。则定其是非。明示今后者。岂非其责乎。噫。拯之于棨。自少执业。实有罔极之恩。故拯之祭文。亦以父事称之。其平日恩义。有非寻常师弟之比。而末稍弄得。全出恒情之外。则序文所谓苏张手段者。所以深斥乎此。而至如狼狈之谕。前后章疏。以此目拯者。固已多矣。元非始发于尚夏。而此亦据一世之所共道者也。其所以严义理之辨。发公正之愤者。亦岂出于私好恶而然哉。呜呼。世教渐降。师道日丧。人不知有师弟之伦久矣。而顷年父师轻重之教。又为一大藉重之资。夫以师生之重。并列于君父。而今欲于父师之间。有所轻重。则其将共君父之并尊。而亦有所轩轾耶。今以中庸所谓尊贤亲亲之义言之。父子之伦。其重如何。而苟无师教。则人之异禽兽几希。亦岂知重父子之伦而全父子之恩乎。其或废一。则义理乖而人道绝矣。拯于平日亲炙儒贤之门。亦岂不知无犯无隐之地。不可背悖。而数十年来再蹈一辙。甚至于父事之间。临绝之托。不惟不能奉行。而乃反诿之以不记。尚夏之所深恶而痛斥者。正在此处。故其心以为宁被奎辈无限丑辱。只欲以一
客乎主乎。拯所以处此者。是耶非耶。夫以尚夏之贤。其言足以荣辱一世。则定其是非。明示今后者。岂非其责乎。噫。拯之于棨。自少执业。实有罔极之恩。故拯之祭文。亦以父事称之。其平日恩义。有非寻常师弟之比。而末稍弄得。全出恒情之外。则序文所谓苏张手段者。所以深斥乎此。而至如狼狈之谕。前后章疏。以此目拯者。固已多矣。元非始发于尚夏。而此亦据一世之所共道者也。其所以严义理之辨。发公正之愤者。亦岂出于私好恶而然哉。呜呼。世教渐降。师道日丧。人不知有师弟之伦久矣。而顷年父师轻重之教。又为一大藉重之资。夫以师生之重。并列于君父。而今欲于父师之间。有所轻重。则其将共君父之并尊。而亦有所轩轾耶。今以中庸所谓尊贤亲亲之义言之。父子之伦。其重如何。而苟无师教。则人之异禽兽几希。亦岂知重父子之伦而全父子之恩乎。其或废一。则义理乖而人道绝矣。拯于平日亲炙儒贤之门。亦岂不知无犯无隐之地。不可背悖。而数十年来再蹈一辙。甚至于父事之间。临绝之托。不惟不能奉行。而乃反诿之以不记。尚夏之所深恶而痛斥者。正在此处。故其心以为宁被奎辈无限丑辱。只欲以一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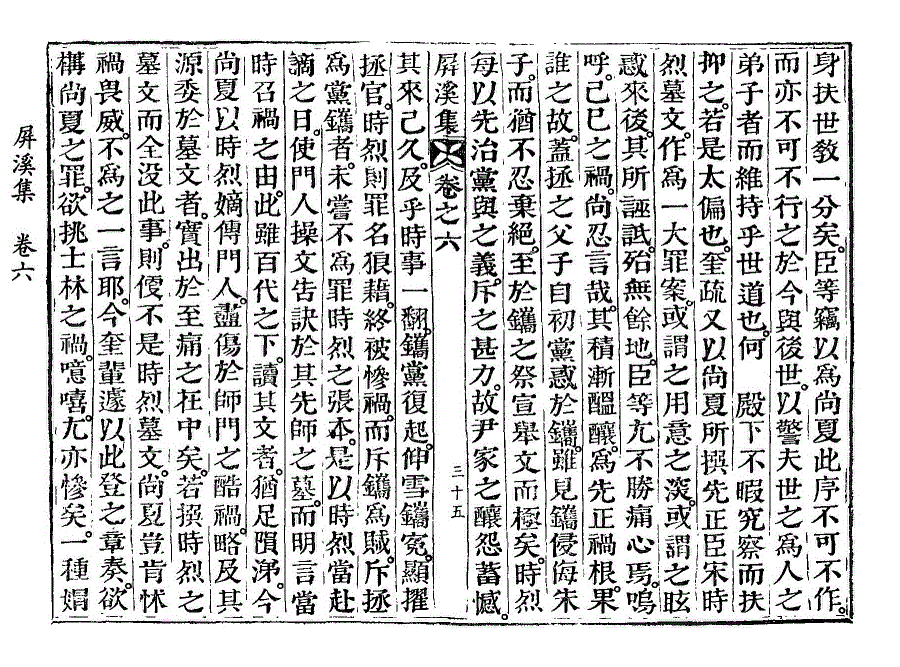 身扶世教一分矣。臣等窃以为尚夏此序不可不作。而亦不可不行之于今与后世。以警夫世之为人之弟子者而维持乎世道也。何 殿下不暇究察而扶抑之。若是太偏也。奎疏又以尚夏所撰先正臣宋时烈墓文。作为一大罪案。或谓之用意之深。或谓之眩惑来后。其所诬诋。殆无馀地。臣等尤不胜痛心焉。呜呼。己巳之祸。尚忍言哉。其积渐酝酿。为先正祸根。果谁之故。盖拯之父子自初党惑于鑴。虽见鑴侵侮朱子。而犹不忍弃绝。至于鑴之祭宣举文而极矣。时烈每以先治党与之义。斥之甚力。故尹家之酿怨蓄憾。其来已久。及乎时事一翻。鑴党复起。伸雪鑴冤。显擢拯官。时烈则罪名狼藉。终被惨祸。而斥鑴为贼。斥拯为党鑴者。未尝不为罪时烈之张本。是以时烈当赴谪之日。使门人操文告诀于其先师之墓。而明言当时召祸之由。此虽百代之下。读其文者。犹足陨涕。今尚夏以时烈嫡传门人。衋伤于师门之酷祸。略及其源委于墓文者。实出于至痛之在中矣。若撰时烈之墓文而全没此事。则便不是时烈墓文。尚夏岂肯怵祸畏威。不为之一言耶。今奎辈遽以此登之章奏。欲构尚夏之罪。欲挑士林之祸。噫嘻。尤亦惨矣。一种媢
身扶世教一分矣。臣等窃以为尚夏此序不可不作。而亦不可不行之于今与后世。以警夫世之为人之弟子者而维持乎世道也。何 殿下不暇究察而扶抑之。若是太偏也。奎疏又以尚夏所撰先正臣宋时烈墓文。作为一大罪案。或谓之用意之深。或谓之眩惑来后。其所诬诋。殆无馀地。臣等尤不胜痛心焉。呜呼。己巳之祸。尚忍言哉。其积渐酝酿。为先正祸根。果谁之故。盖拯之父子自初党惑于鑴。虽见鑴侵侮朱子。而犹不忍弃绝。至于鑴之祭宣举文而极矣。时烈每以先治党与之义。斥之甚力。故尹家之酿怨蓄憾。其来已久。及乎时事一翻。鑴党复起。伸雪鑴冤。显擢拯官。时烈则罪名狼藉。终被惨祸。而斥鑴为贼。斥拯为党鑴者。未尝不为罪时烈之张本。是以时烈当赴谪之日。使门人操文告诀于其先师之墓。而明言当时召祸之由。此虽百代之下。读其文者。犹足陨涕。今尚夏以时烈嫡传门人。衋伤于师门之酷祸。略及其源委于墓文者。实出于至痛之在中矣。若撰时烈之墓文而全没此事。则便不是时烈墓文。尚夏岂肯怵祸畏威。不为之一言耶。今奎辈遽以此登之章奏。欲构尚夏之罪。欲挑士林之祸。噫嘻。尤亦惨矣。一种媢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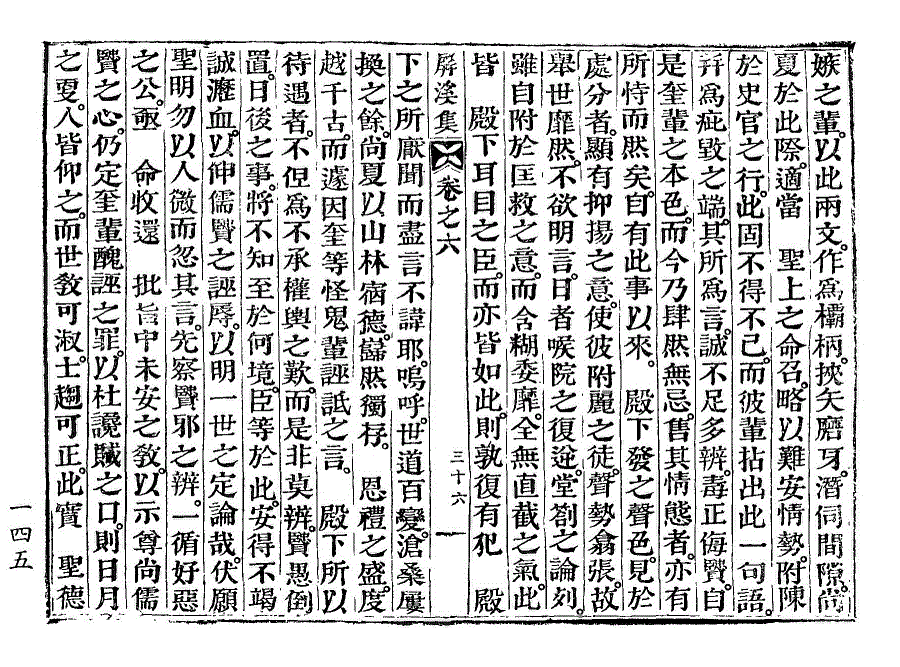 嫉之辈。以此两文。作为𣠽柄。挟矢磨牙。潜伺间隙。尚夏于此际。适当 圣上之命召。略以难安情势。附陈于史官之行。此固不得不已。而彼辈拈出此一句语。并为疵毁之端。其所为言。诚不足多辨。毒正侮贤。自是奎辈之本色。而今乃肆然无忌。售其情态者。亦有所恃而然矣。自有此事以来。 殿下发之声色。见于处分者。显有抑扬之意。使彼附丽之徒。声势翕张。故举世靡然。不欲明言。日者喉院之复逆。堂劄之论列。虽自附于匡救之意。而含糊委靡。全无直截之气。此皆 殿下耳目之臣。而亦皆如此。则孰复有犯 殿下之所厌闻而尽言不讳耶。呜呼。世道百变。沧桑屡换之馀。尚夏以山林宿德。岿然独存。 恩礼之盛。度越千古。而遽因奎等怪鬼辈诬诋之言。 殿下所以待遇者。不但为不承权舆之叹。而是非莫辨。贤愚倒置。日后之事。将不知至于何境。臣等于此。安得不竭诚沥血。以伸儒贤之诬辱。以明一世之定论哉。伏愿圣明勿以人微而忽其言。先察贤邪之辨。一循好恶之公。亟 命收还 批旨中未安之教。以示尊尚儒贤之心。仍定奎辈丑诬之罪。以杜谗贼之口。则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而世教可淑。士趋可正。此实 圣德
嫉之辈。以此两文。作为𣠽柄。挟矢磨牙。潜伺间隙。尚夏于此际。适当 圣上之命召。略以难安情势。附陈于史官之行。此固不得不已。而彼辈拈出此一句语。并为疵毁之端。其所为言。诚不足多辨。毒正侮贤。自是奎辈之本色。而今乃肆然无忌。售其情态者。亦有所恃而然矣。自有此事以来。 殿下发之声色。见于处分者。显有抑扬之意。使彼附丽之徒。声势翕张。故举世靡然。不欲明言。日者喉院之复逆。堂劄之论列。虽自附于匡救之意。而含糊委靡。全无直截之气。此皆 殿下耳目之臣。而亦皆如此。则孰复有犯 殿下之所厌闻而尽言不讳耶。呜呼。世道百变。沧桑屡换之馀。尚夏以山林宿德。岿然独存。 恩礼之盛。度越千古。而遽因奎等怪鬼辈诬诋之言。 殿下所以待遇者。不但为不承权舆之叹。而是非莫辨。贤愚倒置。日后之事。将不知至于何境。臣等于此。安得不竭诚沥血。以伸儒贤之诬辱。以明一世之定论哉。伏愿圣明勿以人微而忽其言。先察贤邪之辨。一循好恶之公。亟 命收还 批旨中未安之教。以示尊尚儒贤之心。仍定奎辈丑诬之罪。以杜谗贼之口。则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而世教可淑。士趋可正。此实 圣德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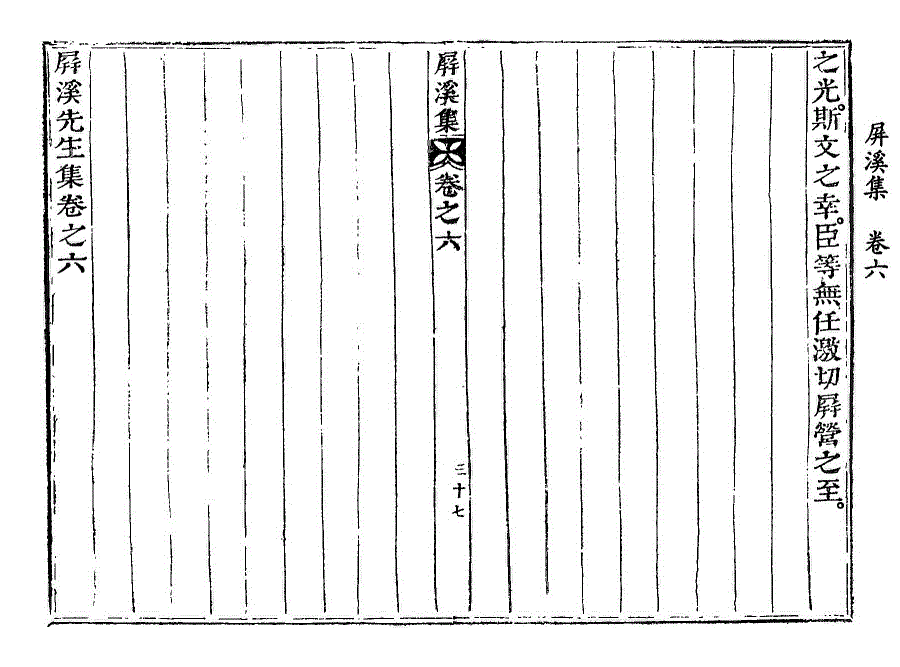 之光。斯文之幸。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之光。斯文之幸。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