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x 页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书(知旧往复)
书(知旧往复)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09H 页
 答金稚明(时粲)大学问目(癸丑十二月)
答金稚明(时粲)大学问目(癸丑十二月)序文分六节
序文分节。如来说推之固得之。然如此等一片文字。当首尾通看。以见其一篇大意之通贯。又逐段细看。以尽其曲折精微之所蕴。不必徒切切于节数之分排。硬定说杀。转动不得。上无以举其大。下无以尽其细也。如此序。通看则大意不出大学之道兴废晦明而已。细看则第二节内盖自一段言性善。然其一段言气质。一有一段言设教。一节之中。又有几节之可分。以此推之。馀可见矣。
补其阙略
采辑放失与补其阙略。各为一事。采辑放失。指整错简补亡章而言。补其阙略。指诚意正心章下注及正心章注敬字之类而言也。经文言欲诚意先致知。欲正心先诚意。而传文此二章。不言诚意之在致知。正心之在诚意。与他章义例不同。此不免为阙略。故章下特言其相须之意以补之。正心章。只言心不在之病。而不言其存心之药方。故章句特言敬字以补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09L 页
 此皆朱先生之己意。而非有前言之沿袭者。即所谓窃附己意。补其阙略者也。放失阙略。相对为说。则所谓放失者。本有此而中经放失之云也。所谓阙略者。本无此而未免阙略之云也。本有此而中经放失。故采其旧而复辑之。本无此而未免阙略。故附己意而新补之。语意极分明。从来读者。只为阙略下小注所误。皆未免错看。尤庵先生说。今未详记。而似亦以补阙为补亡章矣。
此皆朱先生之己意。而非有前言之沿袭者。即所谓窃附己意。补其阙略者也。放失阙略。相对为说。则所谓放失者。本有此而中经放失之云也。所谓阙略者。本无此而未免阙略之云也。本有此而中经放失。故采其旧而复辑之。本无此而未免阙略。故附己意而新补之。语意极分明。从来读者。只为阙略下小注所误。皆未免错看。尤庵先生说。今未详记。而似亦以补阙为补亡章矣。明德
明德者。主言心而包性情在其中。盖心统性情之名也。章句明德之释。所得乎天四字。是说明德之所本。(天字是明德本原。得字是德之张本。)虚灵不昧以下。方说明德之在人者。而虚灵不昧是心。具众理是性。应万事是情。是合心性情而为明德之训也。然具众理应万事。其具之应之者。皆是虚灵不昧者之所为。则此乃心之主性情也。愚故曰明德者。心统性情之名也。单言虚灵不昧。则可以包得其具众理应万事之义。先生所谓只虚灵不昧四字。说明德意已足者。盖以此也。今以虚灵不昧与具众理应万事对说。则一是言心。一是言性。一是言情。不可以相包。而虚灵不昧。只是说心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0H 页
 气而已。若于此三言中。专以虚灵不昧四字训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为虚灵之注脚。则是专以气字当得明德。而以具众理应万事。为气中之所包也。明德果专属气一边物事耶。章句明德者者字与下者也者字。一呼一应。相为终始以成文者也。明德之释。若止于虚灵不昧。而不止于应万事。则上下二者字。不相呼应。不相终始。不成文字。而不复为训诂之体矣。以虚灵不昧四字。划作明德之训。而以具众理应万事。为申言虚灵之所包者。宛转说来。语若无病。而意实有偏。此盖于灵觉上。见得遍重。必欲以灵觉当明德。而又恐灵觉之不能专当明德。则又必以具众理应万事。退作虚灵之注脚。而不得进为明德之训。宁以为明德之所包。而不肯以为明德之实体。其论明德。专主于心而不主于性善。专属于气而不属于理。其流之弊。将不免与释氏本心之学同归矣。释氏灵觉之心。亦何尝不包众理。惟其所见。只在于灵觉。而不在于众理。故不免为异端矣。儒释之分。只在于心性之辨。可不谨哉。高论大槩得之。更以此意推之。则当益见其分晓矣。道心二字。恐亦下得不审。道心专言用而明德兼体用。故不可合论矣。种子二字。亦改
气而已。若于此三言中。专以虚灵不昧四字训明德。而具众理应万事。为虚灵之注脚。则是专以气字当得明德。而以具众理应万事。为气中之所包也。明德果专属气一边物事耶。章句明德者者字与下者也者字。一呼一应。相为终始以成文者也。明德之释。若止于虚灵不昧。而不止于应万事。则上下二者字。不相呼应。不相终始。不成文字。而不复为训诂之体矣。以虚灵不昧四字。划作明德之训。而以具众理应万事。为申言虚灵之所包者。宛转说来。语若无病。而意实有偏。此盖于灵觉上。见得遍重。必欲以灵觉当明德。而又恐灵觉之不能专当明德。则又必以具众理应万事。退作虚灵之注脚。而不得进为明德之训。宁以为明德之所包。而不肯以为明德之实体。其论明德。专主于心而不主于性善。专属于气而不属于理。其流之弊。将不免与释氏本心之学同归矣。释氏灵觉之心。亦何尝不包众理。惟其所见。只在于灵觉。而不在于众理。故不免为异端矣。儒释之分。只在于心性之辨。可不谨哉。高论大槩得之。更以此意推之。则当益见其分晓矣。道心二字。恐亦下得不审。道心专言用而明德兼体用。故不可合论矣。种子二字。亦改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0L 页
 作张本等字好矣。心与明德。虽非二物。心有时对性情而言。而明德不可对性情而言。故谓以心包性情则可。而谓以明德包性情则不可矣。
作张本等字好矣。心与明德。虽非二物。心有时对性情而言。而明德不可对性情而言。故谓以心包性情则可。而谓以明德包性情则不可矣。虚灵字欠了明字之意。故加不昧二字。以足其意。来说亦已得之。
因其所发而遂明之
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一句。实包动静工夫。动时固无可论。至于静时。亦必因明德之发见而下得工夫。须先知静时之当存养。而又欲其存养。然后方可下得存养之功。其知而欲之者。即所谓明德之发见也。因其知而欲之之心。下得存养之功者。即所谓因其发而明之者也。此其因所发一句。所以包得动静工夫也。读者不察此意。遂以为大学一书无静时工夫。则其害于理大矣。不是文义间小失也。大学一书。规模极大。节目详备。岂反遗此涵养一节本领工夫耶。若果无涵养一节。则所谓明明德。只明得一半而不能明其全体。其所未明之一半。又是本原之所在。则若是而可谓明德之止于至善乎。若谓涵养之功。已具于小学之教。大学之教。虽无此一节。亦不为欠阙云尔。则依靠前日之教。欠阙目下之功者。决非圣人设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1H 页
 教之意。且若然尔。则大学之所已言。中庸将不可言。孔子之所已言。孟子将不得言也。先生所谓涵养德性。已在小学。故大学工夫。只自格致说起者。此亦大纲说为学次第耳。岂谓自乡人以至于圣人。自修身以至于平天下。其本领工夫。全靠十五岁以前事。而十五岁以后。不复作此工夫耶。篇内正心一章。正是说静时工夫。而亦包在此因所发之中矣。高见已知其明德工夫之该动静。则亦易见得到此。幸更以此意推详之如何。
教之意。且若然尔。则大学之所已言。中庸将不可言。孔子之所已言。孟子将不得言也。先生所谓涵养德性。已在小学。故大学工夫。只自格致说起者。此亦大纲说为学次第耳。岂谓自乡人以至于圣人。自修身以至于平天下。其本领工夫。全靠十五岁以前事。而十五岁以后。不复作此工夫耶。篇内正心一章。正是说静时工夫。而亦包在此因所发之中矣。高见已知其明德工夫之该动静。则亦易见得到此。幸更以此意推详之如何。定静安虑
知止能得。为知行大分。而定静安虑。只是中间脉络之相因者也。不必深看而切切分配于知行也。然就其中细分之。则自知至安。是事未来前事。而知止为知。定静安似有行底意思。自虑至得。是事已来后事。而虑复为知。得为行。然定静安。皆因知止。而然定是知之定。静安又是知之静安。则三字皆属知一边。乃为可耳。定静安虑。皆当属心。此则来说是矣。
致知
致知之知。所知之知。只是一知也。但致知之知。举全体而言。所知之知。逐事而言。有大小偏全之不同耳。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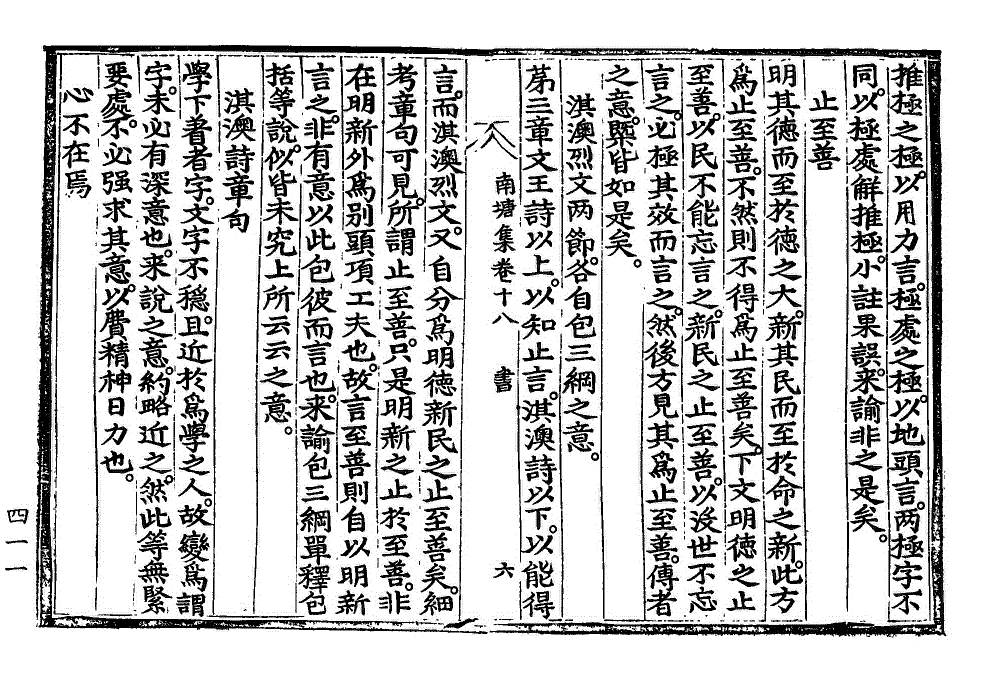 推极之极。以用力言。极处之极。以地头言。两极字不同。以极处解推极。小注果误。来谕非之是矣。
推极之极。以用力言。极处之极。以地头言。两极字不同。以极处解推极。小注果误。来谕非之是矣。止至善
明其德而至于德之大。新其民而至于命之新。此方为止至善。不然则不得为止至善矣。下文明德之止至善。以民不能忘言之。新民之止至善。以没世不忘言之。必极其效而言之。然后方见其为止至善。传者之意。槩皆如是矣。
淇澳烈文两节。各自包三纲之意。
第三章文王诗以上。以知止言。淇澳诗以下。以能得言。而淇澳烈文。又自分为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矣。细考章句可见。所谓止至善。只是明新之止于至善。非在明新外为别头项工夫也。故言至善则自以明新言之。非有意以此包彼而言也。来谕包三纲单释包括等说。似皆未究上所云云之意。
淇澳诗章句
学下着者字。文字不稳。且近于为学之人。故变为谓字。未必有深意也。来说之意。约略近之。然此等无紧要处。不必强求其意。以费精神日力也。
心不在焉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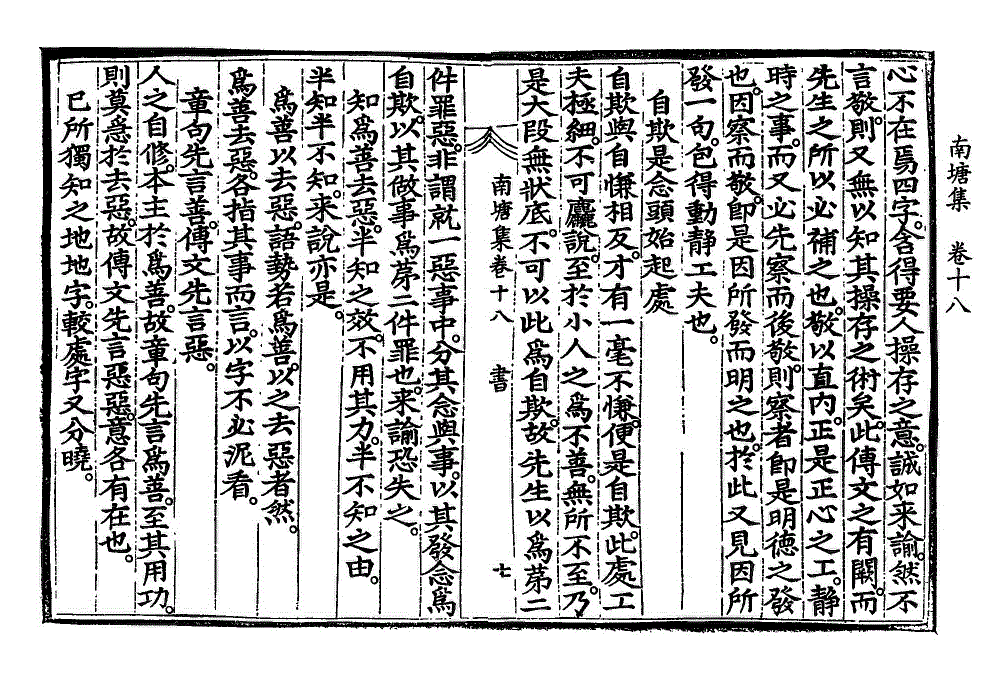 心不在焉四字。含得要人操存之意。诚如来谕。然不言敬。则又无以知其操存之术矣。此传文之有阙。而先生之所以必补之也。敬以直内。正是正心之工。静时之事。而又必先察而后敬。则察者即是明德之发也。因察而敬。即是因所发而明之也。于此又见因所发一句。包得动静工夫也。
心不在焉四字。含得要人操存之意。诚如来谕。然不言敬。则又无以知其操存之术矣。此传文之有阙。而先生之所以必补之也。敬以直内。正是正心之工。静时之事。而又必先察而后敬。则察者即是明德之发也。因察而敬。即是因所发而明之也。于此又见因所发一句。包得动静工夫也。自欺是念头始起处
自欺与自慊相反。才有一毫不慊。便是自欺。此处工夫极细。不可粗说。至于小人之为不善。无所不至。乃是大段无状底。不可以此为自欺。故先生以为第二件罪恶。非谓就一恶事中。分其念与事。以其发念为自欺。以其做事为第二件罪也。来谕恐失之。
知为善去恶。半知之效。不用其力。半不知之由。
半知半不知。来说亦是。
为善以去恶。语势若为善。以之去恶者然。
为善去恶。各指其事而言。以字不必泥看。
章句先言善。传文先言恶。
人之自修。本主于为善。故章句先言为善。至其用功。则莫急于去恶。故传文先言恶恶。意各有在也。
己所独知之地地字。较处字又分晓。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2L 页
 地字处字。俱不害就心上说。但地字较实较安贴。
地字处字。俱不害就心上说。但地字较实较安贴。不谨乎此
不谨乎此之此字。只指诚意工夫而言而已。明应上心体之明云云。不谨乎此。应上则其所发云云。何谓无来历耶。
有所之有。非留滞之病。一有之有。非存字之义。
四有所。正是前事已过。后事未来之时。留滞期待之病也。当此事物未接之时。去其留滞期待之病。则此心复其本体之虚明。而为未发之时矣。其主敬存心。去此有所之病。又是静时工夫也。有所之病。皆因前事之应。而又为后事不正之根本。自前事而言则谓之留滞。自后事而言则谓之期待。只是一病也。章句所谓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或问所谓应之不能无失。不能不与俱往。即指前事之应。而是说有所之源。章句所谓欲动情胜。其用不能不失其正。或问所谓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即指后事之应。而是说有所之害。章句所谓一有之三字。或问所谓喜怒忧惧有动于中者。即指前事已过后事未来之时。而正说有所之病。如是推得。可见留滞之为有所有字之为存留之意也。有字若不作存留之意。则何以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3H 页
 见其为病。有所不为病。则何以为不得其正之本乎。章句一有有字。与上句无字对言。故尤见其为存留之意。若如来说而曰是情人所不能无者。而一有是情。则便能做病云者。是果成说乎。章句之意。盖曰虽是所不能无者。然一或存留之则为病云也。如是方成文字义理矣。中间下一然字。以反上文之意。则可见有之之有。非复前者不能无之有矣。又不曰有此而曰有之。下一之字。其为存留之意益明矣。若此有字果是前者不能无之有。则何以下一然字。以反其意。又何以不曰有此而曰有之耶。章句或问之意。本自分明。每患读者不审。幸更详之。章句或问之说既正。则其他诸说之合不合者。皆当就正于此矣。不可复有所疑贰也。
见其为病。有所不为病。则何以为不得其正之本乎。章句一有有字。与上句无字对言。故尤见其为存留之意。若如来说而曰是情人所不能无者。而一有是情。则便能做病云者。是果成说乎。章句之意。盖曰虽是所不能无者。然一或存留之则为病云也。如是方成文字义理矣。中间下一然字。以反上文之意。则可见有之之有。非复前者不能无之有矣。又不曰有此而曰有之。下一之字。其为存留之意益明矣。若此有字果是前者不能无之有。则何以下一然字。以反其意。又何以不曰有此而曰有之耶。章句或问之意。本自分明。每患读者不审。幸更详之。章句或问之说既正。则其他诸说之合不合者。皆当就正于此矣。不可复有所疑贰也。有所不在两节。略有动静之分。
有所只是浮念之妄动也。浮念动则本体亡。浮念息则本体存。只是一事也。传文心不在。即有所之致。而章句察其不存而敬以直之。正亦所以察其有所而去其有所也。上下二节。未见其有动静之分矣。章句前节下察字。后节下察字。则又未尝以动静分言也。大抵正心。只是息浮念而存本体。去妄动而反至静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3L 页
 者也。与中庸之致中。濂溪之主静。同其为立大本之事。始虽加察。终于静存。不可以始有察之之事。便谓正心为兼动静之目矣。章下注曰。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直内字。正是正心字之替换者也。替换直内字。盖虑正心字之有争端。直内字。虽承察字而言。亦可谓兼动静之目乎。
者也。与中庸之致中。濂溪之主静。同其为立大本之事。始虽加察。终于静存。不可以始有察之之事。便谓正心为兼动静之目矣。章下注曰。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直内字。正是正心字之替换者也。替换直内字。盖虑正心字之有争端。直内字。虽承察字而言。亦可谓兼动静之目乎。正修两节工夫。非有显然等级。
正心一章。即致中之事也。前章言诚意之事。后章言约情之事。其言致和之事亦备矣。由诚意而正心。是由用而反之体也。由正心而约情。是由体而达之用也。用有万变。故言诚意言约情。不一而足。体本于一。故但言正心而已。此其三章之指。部伍段落。历落分明。不可混看。而前后相承之意。又未尝不具于其中矣。且人意未诚之前。不能无私意恶念之发。诚其意则一于善而无恶矣。意既诚则恶念虽绝。而犹不能无浮念之乱中而本体亡焉。正其心则浮念息而本体存矣。心既正则本体虽存。而情之所发。犹不能无偏矣。约其情则发皆中节。而无少差谬矣。正心则极其中而大本立。修身则极其和而达道行。此明明德之止于至善而无以复加者也。此又三章工夫。有浅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4H 页
 深始终之别。而皆当各致其事。不可以此包彼。恃一而废二也。从来读者。不察此意。故其为说。若非支离破碎。则必是鹘突儱侗。来说亦近于信同疑异。喜合恶离。更宜详之。
深始终之别。而皆当各致其事。不可以此包彼。恃一而废二也。从来读者。不察此意。故其为说。若非支离破碎。则必是鹘突儱侗。来说亦近于信同疑异。喜合恶离。更宜详之。九章十章兴字。一释一不释。
前章兴字。是带说过。故章句不释。此章兴字。是絜矩之所本。为一章指义之端。故章句于此。始释其意。
忠信之释。必取明道之言者。循物无违。于絜矩意衬切。
忠信二字之训。章句取舍。来说亦是。
三言得失。得众失众。以见诸事者言。善与不善。以有诸己者言。忠信骄泰。以存诸心者言。始言事。次言身。次言心。一节密一节。
章句三言得失。来说推得极分明。
絜矩章。朱子分八节。
此章大旨总论推说亦好。然与章句之旨微不同。但可备一说。不可将作正意压过了章句之说也。顷岁遇一少论称有经学之功者。其论正如此。举而问于愚曰。朱子此章之说。未见其必然。故如此解之云云。愚答曰。愚亦尝推得如此。至于成说。然细思之。终不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4L 页
 如章句之说分明与传文合者。此或可备一说。而不可以此易章句之说。彼意殊不以为然。彼一边气习。槩如是。殊可痛矣。愚之对彼。不讳鄙见。有若与彼争高者。盖彼得此一说。便自以为高妙独得之见。而谓可以突过朱子之上头。故言其他人之见。亦已及此。不足为高妙独得之见。以折其自大之心傲慢之气耳。后来其人极狼狈。甚恨当时犹不能痛斥之也。
如章句之说分明与传文合者。此或可备一说。而不可以此易章句之说。彼意殊不以为然。彼一边气习。槩如是。殊可痛矣。愚之对彼。不讳鄙见。有若与彼争高者。盖彼得此一说。便自以为高妙独得之见。而谓可以突过朱子之上头。故言其他人之见。亦已及此。不足为高妙独得之见。以折其自大之心傲慢之气耳。后来其人极狼狈。甚恨当时犹不能痛斥之也。答金稚明(戊午正月)
投示明史。一阅奉完。观其编缉无法。予夺不公。来谕所谓无足深玩者诚得之。然其为世道之害。则不但止于无可玩而已。其大者。以 永乐靖难之举为不非。而专罪齐黄。至以隐太子巢刺王。为不得不除。以李贤,张居正之起复为不非。而以章纶,吴中行持正之论为不是。是皆于君臣父子之道。有所不明。而论道学。则盛推阳明以为理学。文章光焰万丈。大者如此。馀可知矣。至于 弘光以后。黜其帝号。以虏清直接 崇祯后正统。此是晋史自帝魏。固无足责。而但惜其史之出于朱姓之人。独其论 万历以后。言路势成。专以攻宰相讦边臣为务。终至于误国者。此最得之。足为后来之戒。而其实任用失宜。听纳不明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5H 页
 致。则亦不得为探本之论矣。大抵二百七十馀年间。直是胡乱做去。无一事可以扶植世道。固结人心者。而上专以诛杀为事。下专以贪黩成风。终至于一夫倡乱。四海土崩。其失盖专在于开刱之初。王祎之言。不见用也。而史氏之论。不及于此。亦见其知识之昧昧。 洪武人物。王祎最贤。可作宰相。而摈弃不用。一人之用舍。而治乱之源系焉。则可不慎欤。以其时之近也。故可作鉴戒于今日者甚多。有他日劝讲之责者。恐不可不反覆之也。因笔漫及。不能尽。
致。则亦不得为探本之论矣。大抵二百七十馀年间。直是胡乱做去。无一事可以扶植世道。固结人心者。而上专以诛杀为事。下专以贪黩成风。终至于一夫倡乱。四海土崩。其失盖专在于开刱之初。王祎之言。不见用也。而史氏之论。不及于此。亦见其知识之昧昧。 洪武人物。王祎最贤。可作宰相。而摈弃不用。一人之用舍。而治乱之源系焉。则可不慎欤。以其时之近也。故可作鉴戒于今日者甚多。有他日劝讲之责者。恐不可不反覆之也。因笔漫及。不能尽。与韩审理使(翼谟○乙丑三月)
战船营造给费事。前已奉闻之矣。所可證者。刘晏说也。行中想未有书册可考。故刘说录呈。刘晏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用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以下。不能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馀。船益脆薄。漕军遂废。
战船给费。始颇优厚。屡度裁减。今则其数至少。殆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5L 页
 不足以为计费之给。船工不堪饥困。乞食于村间。此则所尝目见者也。役于官事而乞食村间。事体固为寒心。而船之脆薄。因可推知也。国家备边之具疏虞如此。岂非大可忧者哉。此事不可不变通。纵不能尽复其初。退依刘晏减半犹可之说。其亦可乎。初头优厚。中间裁减。今日所给之数。行关问之则可知矣。
不足以为计费之给。船工不堪饥困。乞食于村间。此则所尝目见者也。役于官事而乞食村间。事体固为寒心。而船之脆薄。因可推知也。国家备边之具疏虞如此。岂非大可忧者哉。此事不可不变通。纵不能尽复其初。退依刘晏减半犹可之说。其亦可乎。初头优厚。中间裁减。今日所给之数。行关问之则可知矣。答申明允(暻○丁卯正月)
先师年谱中未莹二字。论辨之际。意见不合则谓之未莹。自是例语。亦是称停之语也。自古用之。诚不知其为病也。如彼二字。乃是楚山语录中尤翁之说。先师之所记也。后人安敢改动。二者俱不得奉承盛教。悚仄悚仄。
答李伯相(命奭○癸亥九月)
改葬成服。在家者破墓时成服。追到者出柩时成服。似宜。
缌服虽用练布。绞带不练。正服既用练。则其他衣带固无不练之义。而从俗用生布。亦何妨。
妇人应服三年者服缌。亦当受正服。不可只受布带。燕居衣服。恐亦不可但去华盛耳。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6H 页
 祠堂告由。只告当位。则酒果之设。亦独行。
祠堂告由。只告当位。则酒果之设。亦独行。先山若在同局相见之地。则当行告由。
虞祭当在平土后。虽未及成坟。亦无不可。
食素居处受吊。当如丧中。
婚礼。一家无故人代行主礼。来示得之矣。
答李伯相(乙丑)
祖丧中父死。适孙当代服。而父死在练后逼再期。则适孙亦当受衰。而祖之祥日。则以父亡未葬而废祭。诸叔父不得脱服耶。抑设位哭除之而复吉。则当在何时耶。适孙若代服。则当先服祖而后服父耶。既代服则周而除耶。抑通服三年耶。代服祥禫。当以几何为限耶。书疏自称。当以哀孙耶。
祖丧中父死。适孙代服者。虽在练后。父丧成服后。即为祖丧成服。服其馀日。通服三年而除之。与诸父同。祖丧若在父丧未葬之前。则当退行于葬后。而诸父亦不敢先除。有故退行。与闻丧先后不同也。禫则期不过则祭之。过则不祭。此亦诸父同之。书疏当称哀孙。
有为人后者。始于初期受练衰。拟欲再期除之。后闻其非。且祥期已迫。故来问其脱服与加服当否。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6L 页
 此诚难处矣。禫以过时不行。则复吉在何时耶。
此诚难处矣。禫以过时不行。则复吉在何时耶。为人后者受服事。当初大段失礼。今难为说矣。大抵礼曹公文到日。即当发丧成服。今于初期始受服。而再期除之。则是不服三年也。服之练与不练。又不暇论也。如欲追补。自初期始受服日。为服丧之始。计满二十七月而除之。再期前虽有数日。更制麻衰而服之。再期日变除受练服。三期日受禫服。庶或近之。然此出于臆见。何敢教人行之耶。
庶孽之有嫡母者。遭其母丧。当降服耶。抑伸服耶。仪礼则虽云当降。而家礼则不言其降。陶丈则当伸服云。此果为不易之论耶。
庶子有嫡母遭母丧。陶庵说可疑。家礼不言降。父在不降母。既从时王之制。故嫡母在。亦不言降其母耶。今当以仪礼为正。
妇女遭重制者。世俗多不制服。只以布带成服。此似苟艰矣。若制服则虽期大功。亦当以大袖长裙为制耶。抑有他制之合礼者耶。
妇人服制。来说甚是。若不用大袖长裙。则当用上衰下裳之制矣。
答李伯相(丙寅三月)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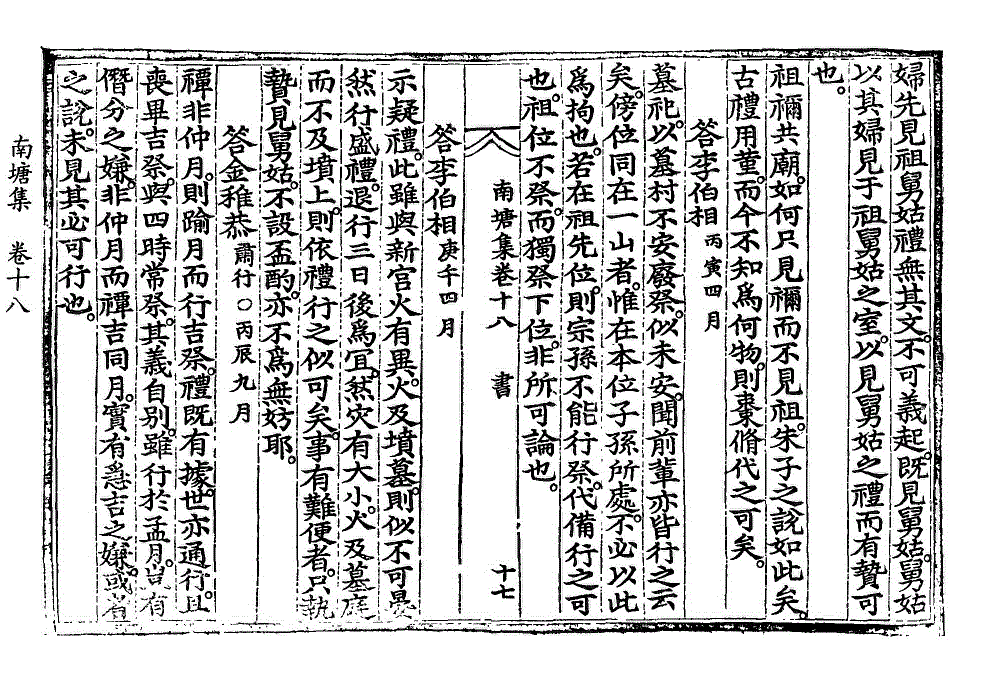 妇先见祖舅姑礼无其文。不可义起。既见舅姑。舅姑以其妇见于祖舅姑之室。以见舅姑之礼而有贽可也。
妇先见祖舅姑礼无其文。不可义起。既见舅姑。舅姑以其妇见于祖舅姑之室。以见舅姑之礼而有贽可也。祖祢共庙。如何只见祢而不见祖。朱子之说如此矣。古礼用堇。而今不知为何物。则枣脩代之可矣。
答李伯相(丙寅四月)
墓祀。以墓村不安废祭。似未安。闻前辈亦皆行之云矣。傍位同在一山者。惟在本位子孙所处。不必以此为拘也。若在祖先位。则宗孙不能行祭。代备行之可也。祖位不祭。而独祭下位。非所可论也。
答李伯相(庚午四月)
示疑礼。此虽与新宫火有异。火及坟墓。则似不可晏然行盛礼。退行三日后为宜。然灾有大小。火及墓庭而不及坟上。则依礼行之似可矣。事有难便者。只执贽见舅姑。不设杯酌。亦不为无妨耶。
答金稚恭(肃行○丙辰九月)
禫非仲月。则踰月而行吉祭。礼既有据。世亦通行。且丧毕吉祭。与四时常祭。其义自别。虽行于孟月。岂有僭分之嫌。非仲月而禫吉同月。实有急吉之嫌。或者之说。未见其必可行也。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7L 页
 答金子静(亮行○壬戌七月)
答金子静(亮行○壬戌七月)危微二字。若是带病说者。则凡人二心危微。而圣人二心不危微否。或谓圣人二心虽安著。而其情状犹自危微。此说如何。
中庸序。既以安著二字。对下危微二字。则圣人心上。恐不可复言危微也。
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者。是谓专守其道心之正耶。抑谓于人道二者。皆守其本心之正耶。
本心之正。并包人道二者而言。
常使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者。是即精一之义耶。抑是精一以后事否。
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即是精一以后事。
二心宜不容一时并发。而今谓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似有二心并发之嫌。未知如何。或有始终先后之可言者耶。
人心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之发。即道心之所行也。朱子所谓乡党所记。皆是人心之发。而浑是道心。栗翁所谓圣人人心即道心。皆谓此也。岂有二心相对并发之理耶。
圣人人心不待道心节制而自得其正。则何以见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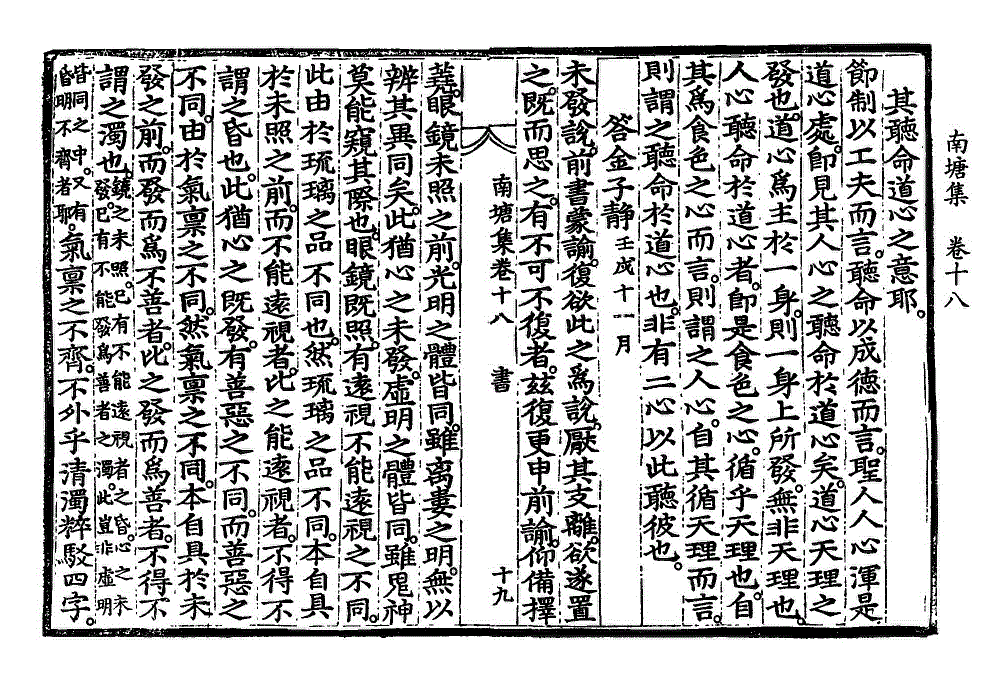 其听命道心之意耶。
其听命道心之意耶。节制以工夫而言。听命以成德而言。圣人人心浑是道心处。即见其人心之听命于道心矣。道心天理之发也。道心为主于一身。则一身上所发。无非天理也。人心听命于道心者。即是食色之心。循乎天理也。自其为食色之心而言。则谓之人心。自其循天理而言。则谓之听命于道心也。非有二心以此听彼也。
答金子静(壬戌十一月)
未发说。前书蒙谕。复欲此之为说。厌其支离。欲遂置之。既而思之。有不可不复者。玆复更申前谕。仰备择荛。眼镜未照之前。光明之体皆同。虽离娄之明。无以辨其异同矣。此犹心之未发。虚明之体皆同。虽鬼神莫能窥其际也。眼镜既照。有远视不能远视之不同。此由于琉璃之品不同也。然琉璃之品不同。本自具于未照之前。而不能远视者。比之能远视者。不得不谓之昏也。此犹心之既发。有善恶之不同。而善恶之不同。由于气禀之不同。然气禀之不同。本自具于未发之前。而发而为不善者。比之发而为善者。不得不谓之浊也。(镜之未照。已有不能远视者之昏。心之未发。已有不能发为善者之浊。此岂非虚明皆同之中。又有昏明不齐者耶。)气禀之不齐。不外乎清浊粹驳四字。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8L 页
 而未发之时。气之偏全强弱。未尝不自在。但不用事耳。此即所谓粹驳之不齐也。粹驳之不齐既如此。则昏明清浊之不齐。亦可反隅而知之矣。盖湛然虚明。未发气像也。清浊粹驳。气禀本色也。未发气像虽同。气禀本色自异。听者不察于此。每以湛然虚明中。有气禀昏明之不齐者为疑。虽以贤者之相信。犹不能无听莹者。则理之难明。果若是耶。大抵未发时大本一说也。湛然虚明一说也。气禀不齐一说也。大本专以理言。但于虚明时其体可见。故必于未发而言之也。湛然虚明。气禀不齐。皆以气言。而湛然虚明。是言未发气像。朱子所谓心之本体。(朱子曰。虚灵只是心之本体。见语类。)指此而言也。气禀不齐。是言气禀本色。朱子所谓心有善恶。(朱子曰。性无不善。心有善恶。若言气质之性则亦有不善。见语类。)亦以此而言也。于此三说者。见得条理分明而不相妨害。则可无疑于纷纷之说矣。
而未发之时。气之偏全强弱。未尝不自在。但不用事耳。此即所谓粹驳之不齐也。粹驳之不齐既如此。则昏明清浊之不齐。亦可反隅而知之矣。盖湛然虚明。未发气像也。清浊粹驳。气禀本色也。未发气像虽同。气禀本色自异。听者不察于此。每以湛然虚明中。有气禀昏明之不齐者为疑。虽以贤者之相信。犹不能无听莹者。则理之难明。果若是耶。大抵未发时大本一说也。湛然虚明一说也。气禀不齐一说也。大本专以理言。但于虚明时其体可见。故必于未发而言之也。湛然虚明。气禀不齐。皆以气言。而湛然虚明。是言未发气像。朱子所谓心之本体。(朱子曰。虚灵只是心之本体。见语类。)指此而言也。气禀不齐。是言气禀本色。朱子所谓心有善恶。(朱子曰。性无不善。心有善恶。若言气质之性则亦有不善。见语类。)亦以此而言也。于此三说者。见得条理分明而不相妨害。则可无疑于纷纷之说矣。又据程子释生之谓性。朱子释程子说。(程子说见近思录。朱子说见答严时亨书。)则人生而静。未发时。不可谓无气质之性矣。既谓有气质之性。则不可谓无不齐矣。既谓有不齐。则又不可谓有粹驳之不齐。而无清浊之不齐也。此理昭然。如指诸掌。不知疑者疑在甚处。谓未发无气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9H 页
 质之性者。是以本然气质判为二性。而二性则二本也。谓心之气质纯善者。是既有性善。又有心善而善有二本矣。况人心有觉。道体无为。则心善之为本。又有大于性善矣。二本固误。而心之为大本尤误。故愚尝深辨之。今于高明半齐半不齐之说。又出此辨。辨亦支离矣。然孟子好辩。韩子好胜。皆非得已也。愚虽无孟,韩之道。其志则固自孟,韩门庭中来矣。听者果能恕之否乎。
质之性者。是以本然气质判为二性。而二性则二本也。谓心之气质纯善者。是既有性善。又有心善而善有二本矣。况人心有觉。道体无为。则心善之为本。又有大于性善矣。二本固误。而心之为大本尤误。故愚尝深辨之。今于高明半齐半不齐之说。又出此辨。辨亦支离矣。然孟子好辩。韩子好胜。皆非得已也。愚虽无孟,韩之道。其志则固自孟,韩门庭中来矣。听者果能恕之否乎。愚于未发之说。辨之屡矣。言者自觉支离。听者宜以为好辩不已也。然其与巍岩辨。初辨其未发无气质之性。再辨其心之气质纯善。三辨其心与气质有辨。与玉溪辨。辨其未发时气质之性纯善。今为高明言之。则辨其未发气质有粹驳之不齐而无清浊之不齐也。人之言各异。故此之辨亦异。非直一说而屡辨也。
危微之说。顷对弘甫。其意有未释然者。弘甫之意。盖以为人心之本色危也。道心之本色微也。在圣人。虽安虽著。其本色之危微则与众人同也。此其思之深而察之密。未可以口舌取服也。然此有一说可破其疑。本色即本初之谓也。本初之圣凡皆同者。皆以善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19L 页
 言。而圣人全其本初。君子复其本初也。危微果是圣凡皆同之本初。则学者当只复其本初之危微。而圣人之不危不微者。乃失其本初也耶。若曰人心道心之发皆气也。故自其本初。已有危动微昧者。则危动微昧。乃是不好底。圣人何以有此不好底本初耶。既是气发。则气必不齐。又安有圣凡皆同之理也。弘甫相见。更以此问之也。弘甫此说。极有意思。极有精彩。有可以感动得人者。而其弊将至于任人心之自危。安道心之日微。以为当然矣。故复言之。
言。而圣人全其本初。君子复其本初也。危微果是圣凡皆同之本初。则学者当只复其本初之危微。而圣人之不危不微者。乃失其本初也耶。若曰人心道心之发皆气也。故自其本初。已有危动微昧者。则危动微昧。乃是不好底。圣人何以有此不好底本初耶。既是气发。则气必不齐。又安有圣凡皆同之理也。弘甫相见。更以此问之也。弘甫此说。极有意思。极有精彩。有可以感动得人者。而其弊将至于任人心之自危。安道心之日微。以为当然矣。故复言之。与金子静(癸亥正月)
巍岩往复文字。久在几下。今已尽阅而细商之否。前书有如在烟海之语。此固然矣。义理之辨。略则理不尽。详则意反晦。此所以难于立说也。然略说以举其大纲。详说以尽其曲折。二者并观。则理于是可明矣。前去文字已详矣。且复略提其要而言之。今之为人物性同之论者。其说不过两端耳。一则以为五常即太极之理也。万物皆具太极。则亦皆具五常也。殊不知太极超形气而称之。五常因气质而名之。(朱子曰。太极超然专说得理。见语类。又曰。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之。见答林德久书。)超形气而称之。故万物同具。因气质而名之。故人物异禀。其名义亦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0H 页
 各不同矣。然太极之理。因气质而言则为五常。五常之理。超形气而言则为太极。亦非有二理也。一则以为万物之生。皆具五行之气。既具五行之气。则自具五行之理。而五理即五常也。殊不知五常乃是五行秀气之理而粹然至善者也。(太极图说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其下方言五性。告子辑注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人得其秀。故其理为五常之德。物不得其秀。则其理亦不得为五常之德。虎狼惟于木之气得其秀。故其理为父子之仁。蜂蚁惟于金之气得其秀。故其理为君臣之义。而其他则不得其秀。故其理不得为五常之德也。凡物有理者。皆可谓五常之德。则彼虎狼之搏噬。蜂虿之毒螫。亦皆有其理矣。此亦可谓五常粹然之德乎。在搏噬者不过为搏噬之理。在毒螫者不过为毒螫之理耳。为此说者。亦非不知其说之有穷也。惟知其有穷。故太极之说见穷。则又为五气之说。而不得于太极上究竟其说。五气之说见穷。则还又为太极之说。而不得于五气上究竟其说。反覆枝拄。互相逃闪。一如小儿迷藏之戏。此所谓遁辞。知其所穷也。前日之辨虽多。其大要不过如此而已。更观此纸而回教之。
各不同矣。然太极之理。因气质而言则为五常。五常之理。超形气而言则为太极。亦非有二理也。一则以为万物之生。皆具五行之气。既具五行之气。则自具五行之理。而五理即五常也。殊不知五常乃是五行秀气之理而粹然至善者也。(太极图说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其下方言五性。告子辑注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人得其秀。故其理为五常之德。物不得其秀。则其理亦不得为五常之德。虎狼惟于木之气得其秀。故其理为父子之仁。蜂蚁惟于金之气得其秀。故其理为君臣之义。而其他则不得其秀。故其理不得为五常之德也。凡物有理者。皆可谓五常之德。则彼虎狼之搏噬。蜂虿之毒螫。亦皆有其理矣。此亦可谓五常粹然之德乎。在搏噬者不过为搏噬之理。在毒螫者不过为毒螫之理耳。为此说者。亦非不知其说之有穷也。惟知其有穷。故太极之说见穷。则又为五气之说。而不得于太极上究竟其说。五气之说见穷。则还又为太极之说。而不得于五气上究竟其说。反覆枝拄。互相逃闪。一如小儿迷藏之戏。此所谓遁辞。知其所穷也。前日之辨虽多。其大要不过如此而已。更观此纸而回教之。答金子静(癸亥三月)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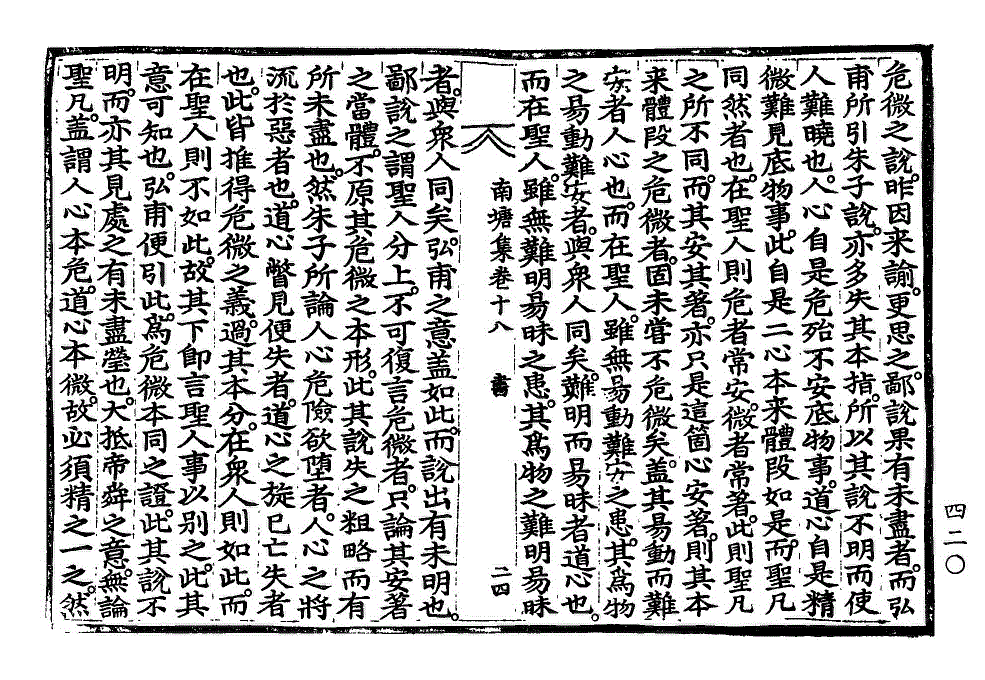 危微之说。昨因来谕。更思之。鄙说果有未尽者。而弘甫所引朱子说。亦多失其本指。所以其说不明而使人难晓也。人心自是危殆不安底物事。道心自是精微难见底物事。此自是二心本来体段如是。而圣凡同然者也。在圣人则危者常安。微者常著。此则圣凡之所不同。而其安其著。亦只是这个心安著。则其本来体段之危微者。固未尝不危微矣。盖其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而在圣人。虽无易动难安之患。其为物之易动难安者。与众人同矣。难明而易昧者道心也。而在圣人。虽无难明易昧之患。其为物之难明易昧者。与众人同矣。弘甫之意盖如此。而说出有未明也。鄙说之谓圣人分上。不可复言危微者。只论其安著之当体。不原其危微之本形。此其说失之粗略而有所未尽也。然朱子所论人心危险欲堕者。人心之将流于恶者也。道心瞥见便失者。道心之旋已亡失者也。此皆推得危微之义。过其本分。在众人则如此。而在圣人则不如此。故其下即言圣人事以别之。此其意可知也。弘甫便引此。为危微本同之證。此其说不明。而亦其见处之有未尽莹也。大抵帝舜之意。无论圣凡。盖谓人心本危。道心本微。故必须精之一之。然
危微之说。昨因来谕。更思之。鄙说果有未尽者。而弘甫所引朱子说。亦多失其本指。所以其说不明而使人难晓也。人心自是危殆不安底物事。道心自是精微难见底物事。此自是二心本来体段如是。而圣凡同然者也。在圣人则危者常安。微者常著。此则圣凡之所不同。而其安其著。亦只是这个心安著。则其本来体段之危微者。固未尝不危微矣。盖其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而在圣人。虽无易动难安之患。其为物之易动难安者。与众人同矣。难明而易昧者道心也。而在圣人。虽无难明易昧之患。其为物之难明易昧者。与众人同矣。弘甫之意盖如此。而说出有未明也。鄙说之谓圣人分上。不可复言危微者。只论其安著之当体。不原其危微之本形。此其说失之粗略而有所未尽也。然朱子所论人心危险欲堕者。人心之将流于恶者也。道心瞥见便失者。道心之旋已亡失者也。此皆推得危微之义。过其本分。在众人则如此。而在圣人则不如此。故其下即言圣人事以别之。此其意可知也。弘甫便引此。为危微本同之證。此其说不明。而亦其见处之有未尽莹也。大抵帝舜之意。无论圣凡。盖谓人心本危。道心本微。故必须精之一之。然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1H 页
 后中可执也云尔。而圣人之生知。即其精之者。安行。即其一之者。圣人亦未尝无精一之事。但其精之一之者。有成德入德之不同耳。如是说得。庶几无偏耶。赖诸贤讲叩不置。得究其未究之论。诚幸诚幸。
后中可执也云尔。而圣人之生知。即其精之者。安行。即其一之者。圣人亦未尝无精一之事。但其精之一之者。有成德入德之不同耳。如是说得。庶几无偏耶。赖诸贤讲叩不置。得究其未究之论。诚幸诚幸。语类论人心曰。危险危动。(危下添一动字险字。则便已将流于恶也。濂溪所谓欲动情胜之动。朱子所谓世路无如人欲险之险是也。)又曰。循人欲。自是危险。动不动。便是堕坑落堑。危孰甚焉。论道心曰。微昧微晦。又曰。惟微是瞥见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此皆并其已流已昧者而言。则盖皆是泛论众人之心。非的论危微二字之义也。中庸序曰。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大全尚书注曰。人心易动而难反。义理难明而易昧。未尝于道心直下晦昧字。人心兼下动险字。则其于危微之本体。未流而易流。未昧而易昧者。说得最为端的矣。(易动易昧。难明难反者。皆未然而将然之辞。非已然之辞也。)语类说。却不如此。而混同看过。不甚区别。所以前说之彼此皆有失也。今却区别如此。庶几知危微之本义。而亦知朱子之说各有所指也。
中庸序文论人心曰。危殆而不安。其下承之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序文论道心曰。微妙而难见。尚书注曰。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此可见圣人之二心。本皆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1L 页
 危微。圣人分上。既言危微。则危微之义。只可平平说过。才带着动险晦昧等字说来。则便非圣人之所同。而非危微之本义也。
危微。圣人分上。既言危微。则危微之义。只可平平说过。才带着动险晦昧等字说来。则便非圣人之所同。而非危微之本义也。答金弘甫(毅行○丙寅四月)
示谕心说。为说虽多端。要其宗旨所在。不过曰心纯善也。人心至善。禅家之宗旨也。宗旨所在如此。则从此演出者。又可知也。况其命文立辞。支离暗杂。迂回破碎。令人莫可寻见其意趣端绪。又安得爬栉而论辨乎。其所解鄙说者。亦皆横拗牵率。添枝接叶。全失其指。见在之人。犹且如此。况于已死之古人乎。窃观盛意。自信甚笃。所守已固。卒难归一。各尊所闻。斯亦可矣。第惟所望者。朱子全书及语类论释氏处。类聚而合观之。庶或有犁然契合者矣。来纸宋士能所见大旨。适与左右同。故欲一示之。姑此留置耳。
凡事皆有纲领大分。纲领正然后。条理可寻。大分明然后。细分可论也。以义理言之。则性理也。心气也。理无不善。气有不善。以学术言之。则吾儒主性。释氏主心。道家主气。此所谓纲领大分也。不识纲领大分。则条理细分。愈究而愈差矣。高明既主心善。则纲领大分。与释氏同矣。纲领大分。既与之同。则条理细分。亦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2H 页
 无一得脱于释氏窠臼矣。此固理势之自然也。今乃曰吾之心善。与释氏心善不同。此果成说。而又是禅家呵佛骂祖之习也。自古为禅学者。何尝不诋释氏而自以为不同耶。
无一得脱于释氏窠臼矣。此固理势之自然也。今乃曰吾之心善。与释氏心善不同。此果成说。而又是禅家呵佛骂祖之习也。自古为禅学者。何尝不诋释氏而自以为不同耶。答金弘甫(丙寅四月)
承谕心说。释氏之论心。亦有曰昏沉跳举。妄心妄觉。何尝专以为纯善耶。只以灵觉为至善。故谓之释氏本心也。来说只以数十字了尽宗旨。而无一字不同释氏。岂愚不解人言而然耶。姑置之。以俟他日更商如何。
附原书
愚亦以为人之心。有虚灵昏昧真妄邪正。虚灵真正。即心之本体而善者也。昏昧邪妄。即心有所拘蔽而恶者也。故但曰心之本体善云尔。未尝直以心为纯善也。
答金弘甫(丙寅六月)
心说屡蒙勤谕。不容不对。释氏之宗旨曰人心至善。不用辛苦修行。其论心体。则曰昭昭灵灵。曰历历孤明。曰主人翁惺惺。此所谓至善者也。其论心之病。则曰昏沉跳举。曰流注妄想。曰把持则云横谷口。放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2L 页
 也。月落寒潭。此于心之体段。何尝不知。只以灵明者为至善。故为异端耳。弘甫之论心。果有一毫差殊于此者乎。释氏之论心。犹以一心言也。弘甫之论心。谓于此心之外。别有气禀拘蔽此心。而谓亦在方寸之中则是亦心也。二心则二性矣。二心二性。释氏之所不道也。(栗谷人心道心图说曰。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又曰。善者清气之发。恶者浊气之发。农岩曰。浊气之发。亦有善情。)又闻弘甫以为若得朱子说明證。岂不信服。其他则不能信服。此言尤可忧也。而多见其不知量也。栗谷之论心性。长书图说。至为明备。无可疑者。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栗谷之笃信朱子如此。故沙溪,尤庵,遂庵,农岩诸先生。亦皆深信栗谷而传守其说。不敢改易。今谓栗谷之说。亦不知朱子之意而不可信。则东方更无可信之人矣。岂亦释氏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者耶。荀卿肆为异论。而李斯出其门。此不可不戒也。(异论。指性恶之论。性恶心善。正好作对。而心善之论。其害甚于性恶。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观于陆氏,王氏则可见也。)
也。月落寒潭。此于心之体段。何尝不知。只以灵明者为至善。故为异端耳。弘甫之论心。果有一毫差殊于此者乎。释氏之论心。犹以一心言也。弘甫之论心。谓于此心之外。别有气禀拘蔽此心。而谓亦在方寸之中则是亦心也。二心则二性矣。二心二性。释氏之所不道也。(栗谷人心道心图说曰。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又曰。善者清气之发。恶者浊气之发。农岩曰。浊气之发。亦有善情。)又闻弘甫以为若得朱子说明證。岂不信服。其他则不能信服。此言尤可忧也。而多见其不知量也。栗谷之论心性。长书图说。至为明备。无可疑者。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栗谷之笃信朱子如此。故沙溪,尤庵,遂庵,农岩诸先生。亦皆深信栗谷而传守其说。不敢改易。今谓栗谷之说。亦不知朱子之意而不可信。则东方更无可信之人矣。岂亦释氏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者耶。荀卿肆为异论。而李斯出其门。此不可不戒也。(异论。指性恶之论。性恶心善。正好作对。而心善之论。其害甚于性恶。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观于陆氏,王氏则可见也。)庄子曰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虚室生白。指心之虚明而言也。吉祥止止。谓虚明为万善之主也。其说心之病。则曰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升而天飞。降而渊沦。又曰。一日而再抚四海之外。异端之论心。盖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3H 页
 皆如此。此非不知心。而只为不知性。故流而为异学也。
皆如此。此非不知心。而只为不知性。故流而为异学也。弘甫之误着。专在于心与气禀之分为二物。心与气禀。既分为二。而气禀又有善恶。则方寸之中。既有性之善。又有心之善。气禀之善恶。部伍重重。而善占三分。恶只占一分矣。然则天下之善人常少而恶人常多何也。气禀之善者。为情之善。恶者为情之恶。而善恶之外无他物。则心之善。独管何事耶。将谓心之善。拘于气禀则为恶。不拘于气禀则为善。则是又与性无别而有性无心可也。有心无性亦可也。自古异端之学。皆坐于心性之无别。不可不明辨也。(释氏,陆氏,王氏直以心为善。告子生之谓性。胡氏性无善恶。虽以性言。亦只以精神知觉言之也。胡氏说。孟子或问详论之矣。○古之圣贤。每以心性分合言之。未有以心与气对言者。分而言之。则心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知觉是也。合而言之。则孟子所谓本心良心仁义之心仁人心是也。而皆主性善而言也。所谓圣人本天也。今以心与气对言。而以心为善。以气为有善恶。则此非释氏本心之学而何哉。朱子言释氏之徒。奋髯切齿谈端绪。瞋目扼腕證本心。弘甫之说良心本心。政如此耳。古人或有以心与气对言者。此气则是血肉形质之气。具于百体者也。)方寸之中谓之心。心与气禀有辨。而同在方寸之中。则方寸之中。亦有非心之物耶。气之在方寸之中者。是为一身之主。而本自无形质。故但谓之神明。神明之气。又有灵而谓之心。则神明与灵。何以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3L 页
 有别。虽有十离朱之明。恐不可以辨得。此是弘甫之宗旨。而直不成说话。直不成义理。
有别。虽有十离朱之明。恐不可以辨得。此是弘甫之宗旨。而直不成说话。直不成义理。明德本合心性言之。而重在于性。观于传文顾諟明命之语及或问论明德处则可见也。今之论明德者。专以虚灵为言。宜其说之流于释氏也。虚灵只指此心灵明处而言。故人人皆同。然虚灵亦属气。气便不齐。故一任其虚灵之所为。则为释氏之猖狂妄行矣。栗谷曰。虚灵底亦有优劣。此亦以虚灵之气禀而言也。
人得正通之气以为心。故其心与禽兽之心不同。正通之气。又有清浊粹驳之分。而圣人之心。得其清粹者。众人之心。得其浊驳者。故圣人众人之心。又有不同也。故朱子曰。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又曰。生知之人。禀气清明。赋质纯粹。此是灼然可信之言。灼然可信之理也。但其心之虚灵。圣凡皆同。故以此虚灵之心。具万善之理。所以为明德也。而才到气禀用事。便有失其明德之本体矣。虚灵如镜之光明。气禀如镜铁之精粗。同在一心。而虚灵气禀所指不同。同在一镜。而光明精粗所指不同。此最譬谕之切近者。譬谕之说。只看其大意。必欲其十分相似。则虽以孟子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4H 页
 长于譬谕者。亦无以开喙矣。(偏正通塞。人物之大分也。清浊粹驳。贤愚之细分也。正通是粗说底。清浊粹驳是精说底。今反以粗说底为心。精说底为气禀。而分作二气。可谓文义之不通矣。正通之与清浊粹驳。只是一气。而谓有精粗说之不同者。正通之气。桀蹠亦禀。而清粹之气。非桀蹠之所禀故也。)
长于譬谕者。亦无以开喙矣。(偏正通塞。人物之大分也。清浊粹驳。贤愚之细分也。正通是粗说底。清浊粹驳是精说底。今反以粗说底为心。精说底为气禀。而分作二气。可谓文义之不通矣。正通之与清浊粹驳。只是一气。而谓有精粗说之不同者。正通之气。桀蹠亦禀。而清粹之气。非桀蹠之所禀故也。)夜气即心之气也。良心即仁义之心也。孟子本以夜气与仁义对说。谓心之夜气清明。则仁义之端发见云也。此与求放心章注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者意同。此岂难晓者耶。弘甫专以灵觉之心为良心。故不得不以夜气别作一气。而并着于方寸之中。以为存此灵觉之地而谓之气禀。真栗谷所谓如此怪语。不曾见于经传者也。(孟子良知。本以仁义之知言之。阳明乃曰。良知者虚灵明觉。本然之体也。此所以为异端也。)
气质有蔽之心。谓心自为其气质所蔽也。古人文字如此言者甚多。本非难解者。朱子栗谷之说。以心为气者。不胜其多。皆置而不论。独于此约略可以东西看者。力主作一大案。而不知其本意之不如此。如此讲论。恐终无益也。
合性与知觉一句。不言气字省文也。非知觉之不可以气言也。栗谷图说曰。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此已以气字代知觉言矣。然弘甫本自不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4L 页
 信栗谷。请且以朱子说言之。朱子答廖子晦书曰。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气聚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此言何谓也。
信栗谷。请且以朱子说言之。朱子答廖子晦书曰。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气聚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此言何谓也。子思曰。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若有昏昧之时。则中亦有昏昧之时耶。朱子答林择之书曰。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大全中言未发。皆此意也。此是未发定论也。语类云云。偶有此一说。而此只以思虑未发者。对思虑已发者而言。别是一义。非子思之本旨极其未发界至十分尽头处而言者也。栗谷之论未发。其说甚详。而专以择之书为主。其后诸贤之说。又皆以栗谷说为主。此是大本所在。不可有异同。于此而有异同。则是不识大本也。
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此特以性情界分而言也。其实天命之性。无时不流行。非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者也。故恶人之心无未发者。谓之中体不立则可也。谓之无性则不可也。此何至积思而不得乎。
栗谷先生曰。明德之体。即至善之体而未发之中也。明德之用。即至善之用而已发之中也。明明德者。即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如此看破。岂不分晓云云。愚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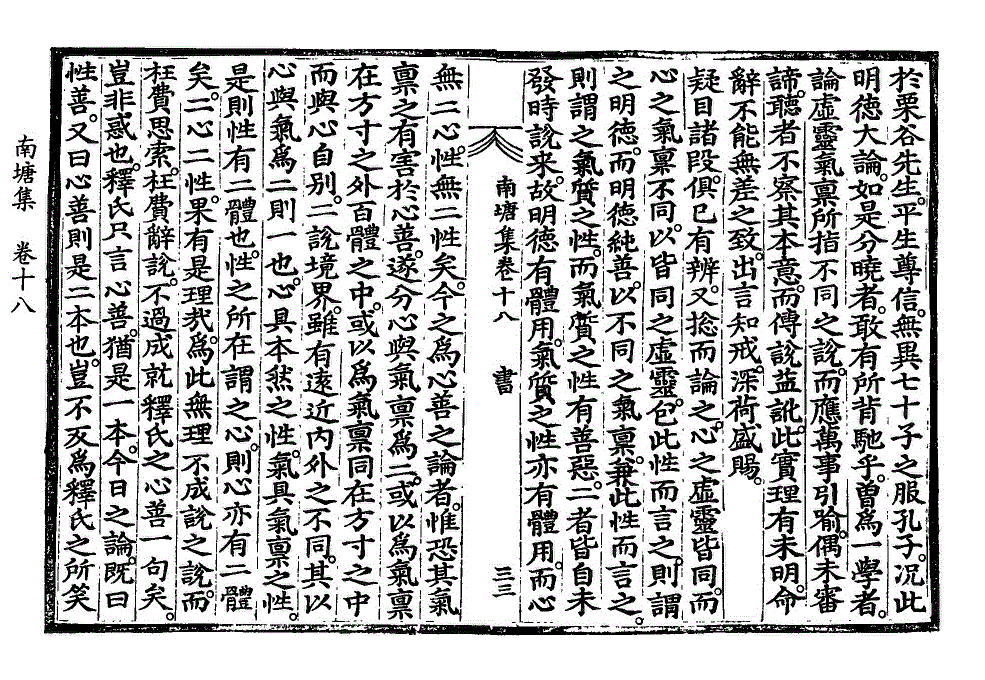 于栗谷先生。平生尊信。无异七十子之服孔子。况此明德大论。如是分晓者。敢有所背驰乎。曾为一学者。论虚灵气禀所指不同之说。而应万事引喻。偶未审谛。听者不察其本意。而传说益讹。此实理有未明。命辞不能无差之致。出言知戒。深荷盛赐。
于栗谷先生。平生尊信。无异七十子之服孔子。况此明德大论。如是分晓者。敢有所背驰乎。曾为一学者。论虚灵气禀所指不同之说。而应万事引喻。偶未审谛。听者不察其本意。而传说益讹。此实理有未明。命辞不能无差之致。出言知戒。深荷盛赐。疑目诸段。俱已有辨。又总而论之。心之虚灵皆同。而心之气禀不同。以皆同之虚灵。包此性而言之。则谓之明德。而明德纯善。以不同之气禀。兼此性而言之。则谓之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有善恶。二者皆自未发时说来。故明德有体用。气质之性亦有体用。而心无二心。性无二性矣。今之为心善之论者。惟恐其气禀之有害于心善。遂分心与气禀为二。或以为气禀在方寸之外百体之中。或以为气禀同在方寸之中而与心自别。二说境界。虽有远近内外之不同。其以心与气为二则一也。心具本然之性。气具气禀之性。是则性有二体也。性之所在谓之心。则心亦有二体矣。二心二性。果有是理哉。为此无理不成说之说。而枉费思索。枉费辞说。不过成就释氏之心善一句矣。岂非惑也。释氏只言心善。犹是一本。今日之论。既曰性善。又曰心善则是二本也。岂不反为释氏之所笑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5L 页
 乎。
乎。答金弘甫(丙寅十一月)
来谕心说。辞不别白。指不分明。老昏无以解见。姑举其大要。更请一言之教。心之与气禀。是一物耶。二物耶。气禀之在方寸之中者。可名为心耶。不可名为心耶。心之为物。是纯善者耶。不纯善者耶。于此明白指谕。使知盛意所在。则亦当献愚矣。来谕又盛推栗谷以为我东之圣人。只此一言。庶有相合之望。幸甚幸甚。然仆之前言。亦非诬也。栗谷心性情图。人心道心图。皆以气质字。着在心圈之中。则是以心与气禀为一也。其说曰。气质则清浊粹驳。有万不同。又曰。善者清气之发。恶者浊气之发。是又以心之气为有清浊也。(心发气发为一发。又见第五长书。)高明前书。以心与气禀为二。而又以心为纯善。栗谷以未发为中。而高明以未发为有不中。此于栗谷之说心性大论。一切不合。故愚以为不信栗谷。不信其言而信其人者。宁有是耶。今日之见。未知如何。而合则谓合。不合则谓不合。不可依违两间。䌤缝说合。使人心悯也。
人物之性。来说得之。然谓有件数之皆全者亦误。朱子每只言牛之顺马之健虎狼之仁蜂蚁之义。何尝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6H 页
 言五数之皆备耶。气相近处。指其理相近者。则亦有五常之彷佛可言者。此乃知觉运动气之相近者。朱子不以此为性矣。
言五数之皆备耶。气相近处。指其理相近者。则亦有五常之彷佛可言者。此乃知觉运动气之相近者。朱子不以此为性矣。心性之说。只有一言可判者。孔子曰。太极生两仪。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者一本也。阴阳者分殊也。心与性。即阴阳太极之谓也。阴阳亦可谓纯善乎。若是纯善。则又一大本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夷子二本故也。不识二本之误。则他不足论也。
心性以理气之分言之。则性理也。心气也。理无不善。而气有不善。以未发已发之分言之。则未发之时。气未用事。故有善无恶。已发之时。气已用事。故有善有恶。虽然。当其未发也。气之清浊粹驳。虽不用事。其气则固自在也。故兼此气而言之。则谓之气质之性而有万不齐。程子所谓才说性时。便不是性是也。朱子,栗谷论未发。皆言未发之时气不用事。不曰未发之时气亦纯善。则其意可见也。
今之论人物不同之性者。皆以为气质善恶之性。今考朱子定论。以人物不同之性为性善得三条。录在下方。
孟子道性善章。或问曰。董子所谓明于天性。知自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6L 页
 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程子所谓知性善。以忠信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谓此也。
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程子所谓知性善。以忠信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谓此也。犬牛人性章。或问曰。予尝以此章之旨。问于李先生。先生曰。孟子之意。只恐其昧于人性之善耳。
性无善无不善章。语类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这便是异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须是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与自家都一般。
与金弘甫(丁卯九月)
心说往复。自高明发之。鄙意则初不欲也。然既已发端。则当毕其说。自往最后书。更未有答。不知何意也。高明所蔽。只在于明德注虚灵二字。今且请以一言了之。虚灵不昧固心也。气禀物欲亦心也。但谓之明德则只指虚灵一边而言。谓之心则并指气禀清浊而言。故谓之心则不同。而谓之明德则皆同也。前日之说大意不出此。今复约而言之如此。回教为望。此是儒释界分生死路头。不可不究其说也。
禹出见罪人。泣曰尧舜之人。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只此一言。可见人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7H 页
 心之不同也。此在史略初卷。人孰不读乎。
心之不同也。此在史略初卷。人孰不读乎。答李生(喜庆○癸丑八月)
每得来书。以先生见谓。自称以门人。心窃不安之甚。玆以情告。幸垂察焉。仆本无德。可堪为人师。是以乡秀后生。或以文字相从。斯名之称。一切辞之。不敢当也。况教之之谓师。学之之谓弟子。斯名之称。岂可苟乎。仆未有教之之事。左右未有学之之事。则斯名之称。又奚自乎。仆与左右相见亦屡矣。实有故旧之谊。书疏往来。但当以故人见处。死生相问足矣。何可辄加以不着之称。以自陷于不诚而取讥于人乎。此后有书。切宜删去此名。以从实去伪。安此之心。至望至望。如其不然。必欲强加之以无实之名。则亦将并与来书而辞之。不复与之通问矣。事至于此。亦非所愿也。仆之为此言。非率然而发也。仆在前日。涉世未久。经事不多。人情世态。皆未能熟知。见人之以文字来问者。辄信其实心而期之以终始。虽加以不着之称。亦不能避也。久而察之。其以实心至者鲜矣。或数年挟册而止。或数次请问而止。其后相见。只叙寒暄道俗事而止耳。不复以文字事见及之。虽或语及文字。退而省其私。未必皆实也。然而旧日之称。犹存而不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7L 页
 去。每听之。未尝不面羞而心愧也。故于后至者。虽不敢逆拒之而不受。至于不着之称。则一切禁绝之。前所往来者。亦皆遍谕之。使改其前日之称谓。此实区区近日自处之实状也。非独于左右而然也。并冀谅察。
去。每听之。未尝不面羞而心愧也。故于后至者。虽不敢逆拒之而不受。至于不着之称。则一切禁绝之。前所往来者。亦皆遍谕之。使改其前日之称谓。此实区区近日自处之实状也。非独于左右而然也。并冀谅察。答朴生(大阳○癸亥九月)
往岁过访。荷意勤矣。今又辱书。益见眷予之深。自愧老丑何以得此于高明也。仍审秋凉。学履清胜。仰慰。仆少不自力。老而无闻。去死不远。将止于此。无足为贤者道也。承有更枉之意。恐贤者未悉此间事也。仆本无学。可以语人者。近又老病。倦于接应。虽复远来。宁有所益。虚名相从。自欺欺人。仆亦耻之。况贤者妙年求道。何以此虚事为哉。学以闻道为至。而道以朝闻夕死为期。此岂可以虚名致之哉。惟愿贤者杜门读书。自力为学。读一书。必了一书之义。了一书。又了一书。有所得焉然后。就有道而正焉。此乃为学之实事也。感贤者有求道之志。而误听于人。虚辱远求。则又恐贤者之失计而重此欺人之过也。故以情仰告。庶几谅之。
与或人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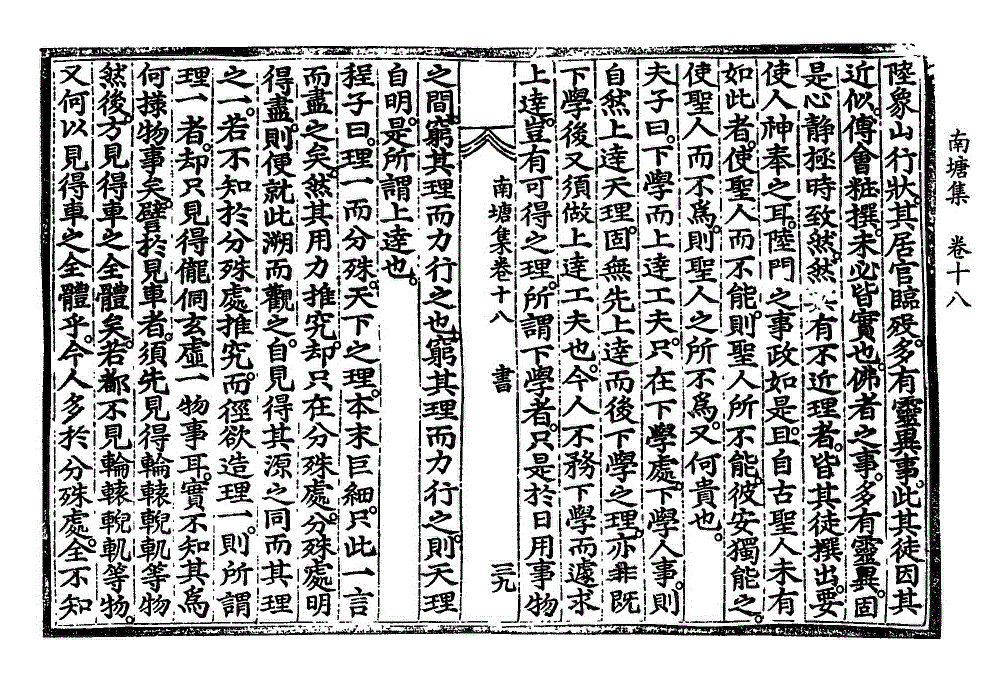 陆象山行状。其居官临殁。多有灵异事。此其徒因其近似。傅会妆撰。未必皆实也。佛者之事。多有灵异。固是心静极时致然。然其有不近理者。皆其徒撰出。要使人神奉之耳。陆门之事政如是。且自古圣人未有如此者。使圣人而不能。则圣人所不能。彼安独能之。使圣人而不为。则圣人之所不为。又何贵也。
陆象山行状。其居官临殁。多有灵异事。此其徒因其近似。傅会妆撰。未必皆实也。佛者之事。多有灵异。固是心静极时致然。然其有不近理者。皆其徒撰出。要使人神奉之耳。陆门之事政如是。且自古圣人未有如此者。使圣人而不能。则圣人所不能。彼安独能之。使圣人而不为。则圣人之所不为。又何贵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工夫。只在下学处。下学人事。则自然上达天理。固无先上达而后下学之理。亦非既下学后又须做上达工夫也。今人不务下学而遽求上达。岂有可得之理。所谓下学者。只是于日用事物之间。穷其理而力行之也。穷其理而力行之。则天理自明。是所谓上达也。
程子曰。理一而分殊。天下之理。本末巨细。只此一言而尽之矣。然其用力推究。却只在分殊处。分殊处明得尽。则便就此溯而观之。自见得其源之同而其理之一。若不知于分殊处推究。而径欲造理一。则所谓理一者。却只见得儱侗玄虚一物事耳。实不知其为何㨾物事矣。譬于见车者。须先见得轮辕輗轨等物然后。方见得车之全体矣。若都不见轮辕輗轨等物。又何以见得车之全体乎。今人多于分殊处。全不知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8L 页
 推究其名义实理。而到底便说一理。此其心则好高自大也。其言则传闻口舌也。而其实则无所见于理一之体矣。
推究其名义实理。而到底便说一理。此其心则好高自大也。其言则传闻口舌也。而其实则无所见于理一之体矣。大抵穷理。只在名言上各究其义。言天则就究其天之所以为天。言地则就究其地之所以为地。言鬼神则必究其如何是鬼。如何是神。言仁义则亦究其名仁者是如何。名义者是如何。自天地万事万物。以至乎一字一句。无不因其名言而究其精蕴。各诣其极而无异吾之所体当者。亦可以各循其则而无所眩乱迷错之患矣。此夫子正名之说。在学者尤为要切。而不特为政者之所先也。
答金始复(癸亥九月)
始复祖母有二子。长子为承重子。次子奉祖母祀。即始复所生父。而始复又以独身。出继伯父之后。生父身后。两代祭祀。生母主之矣。始复方有二子。长子鼎夏既为所后父之孙。次子观夏当还继所生父之后。而第生家无他兄弟。与受无处。继序有缺。故不敢以继后为定。侍养奉祀。礼所不言。所生祖母神主。班附于宗家。有违于礼经。何以则得于意而合于情理耶。尤庵先生曰。为人后者之子。为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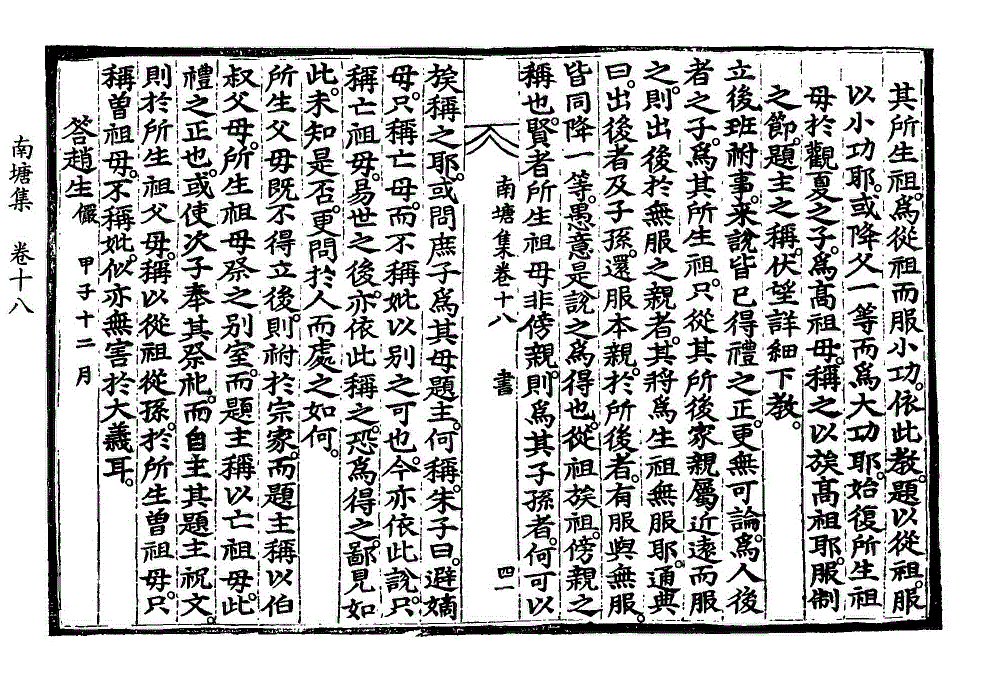 其所生祖。为从祖而服小功。依此教。题以从祖。服以小功耶。或降父一等而为大功耶。始复所生祖母于观夏之子。为高祖母。称之以族高祖耶。服制之节。题主之称。伏望详细下教。
其所生祖。为从祖而服小功。依此教。题以从祖。服以小功耶。或降父一等而为大功耶。始复所生祖母于观夏之子。为高祖母。称之以族高祖耶。服制之节。题主之称。伏望详细下教。立后班祔事。来说皆已得礼之正。更无可论。为人后者之子。为其所生祖。只从其所后家亲属近远而服之。则出后于无服之亲者。其将为生祖无服耶。通典曰。出后者及子孙。还服本亲。于所后者。有服与无服。皆同降一等。愚意是说之为得也。从祖族祖。傍亲之称也。贤者所生祖母非傍亲。则为其子孙者。何可以族称之耶。或问庶子为其母题主。何称。朱子曰。避嫡母。只称亡母。而不称妣以别之可也。今亦依此说。只称亡祖母。易世之后。亦依此称之。恐为得之。鄙见如此。未知是否。更问于人而处之如何。
所生父母既不得立后。则祔于宗家。而题主称以伯叔父母。所生祖母祭之别室。而题主称以亡祖母。此礼之正也。或使次子奉其祭祀。而自主其题主祝文。则于所生祖父母。称以从祖从孙。于所生曾祖母。只称曾祖母。不称妣。似亦无害于大义耳。
答赵生(俨○甲子十二月)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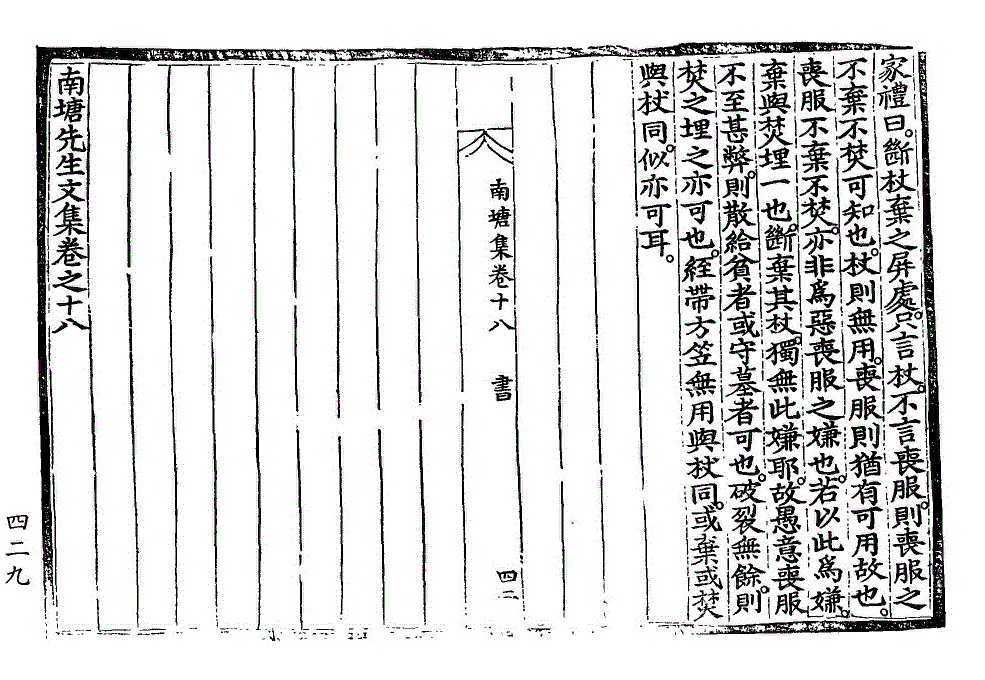 家礼曰。断杖弃之屏处。只言杖。不言丧服。则丧服之不弃不焚可知也。杖则无用。丧服则犹有可用故也。丧服不弃不焚。亦非为恶丧服之嫌也。若以此为嫌。弃与焚埋一也。断弃其杖。独无此嫌耶。故愚意丧服不至甚弊。则散给贫者或守墓者可也。破裂无馀。则焚之埋之亦可也。绖带方笠无用与杖同。或弃或焚与杖同。似亦可耳。
家礼曰。断杖弃之屏处。只言杖。不言丧服。则丧服之不弃不焚可知也。杖则无用。丧服则犹有可用故也。丧服不弃不焚。亦非为恶丧服之嫌也。若以此为嫌。弃与焚埋一也。断弃其杖。独无此嫌耶。故愚意丧服不至甚弊。则散给贫者或守墓者可也。破裂无馀。则焚之埋之亦可也。绖带方笠无用与杖同。或弃或焚与杖同。似亦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