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书(同门往复)
书(同门往复)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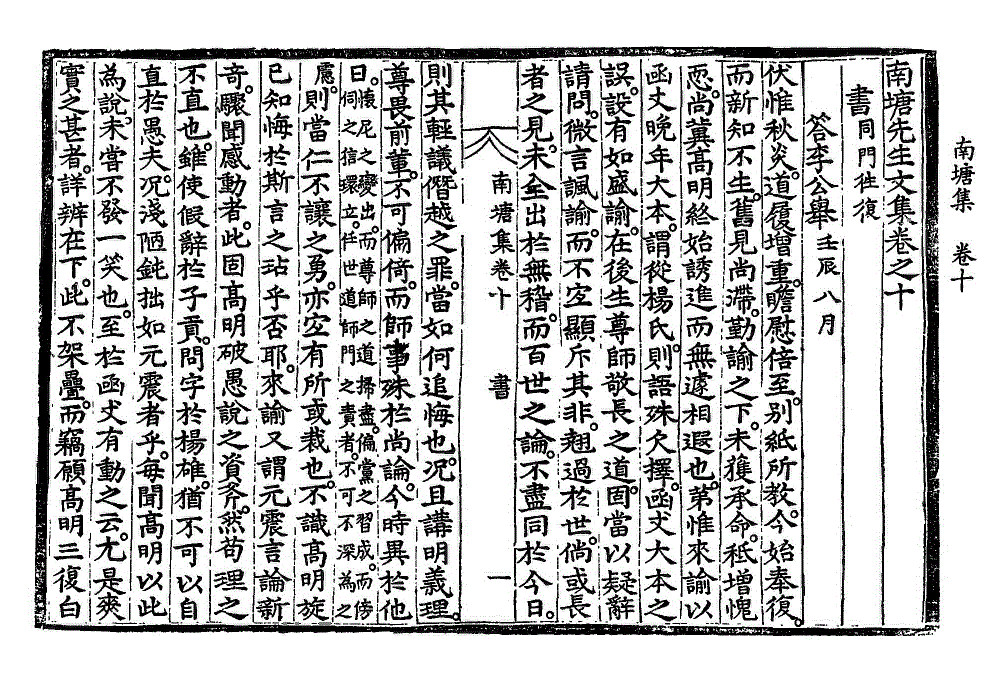 答李公举(壬辰八月)
答李公举(壬辰八月)伏惟秋炎。道履增重。瞻慰倍至。别纸所教。今始奉复。而新知不生。旧见尚滞。勤谕之下。未获承命。秪增愧恧。尚冀高明终始诱进而无遽相遐也。第惟来谕以函丈晚年大本。谓从杨氏。则语殊欠择。函丈大本之误。设有如盛谕。在后生尊师敬长之道。固当以疑辞请问。微言讽谕。而不宜显斥其非。翘过于世。倘或长者之见。未全出于无稽。而百世之论。不尽同于今日。则其轻议僭越之罪。当如何追悔也。况且讲明义理。尊畏前辈。不可偏倚。而师事殊于尚论。今时异于他日。(怀尼之变出。而尊师之道扫尽。偏党之习成。而傍伺之狺环立。任世道师门之责者。不可不深为之虑。)则当仁不让之勇。亦宜有所或裁也。不识高明旋已知悔于斯言之玷乎否耶。来谕又谓元震言论新奇。骤闻感动者。此固高明破愚说之资斧。然苟理之不直也。虽使假辞于子贡。问字于杨雄。犹不可以自直于愚夫。况浅陋钝拙如元震者乎。每闻高明以此为说。未尝不发一笑也。至于函丈有动之云。尤是爽实之甚者。详辨在下。此不架叠。而窃愿高明三复白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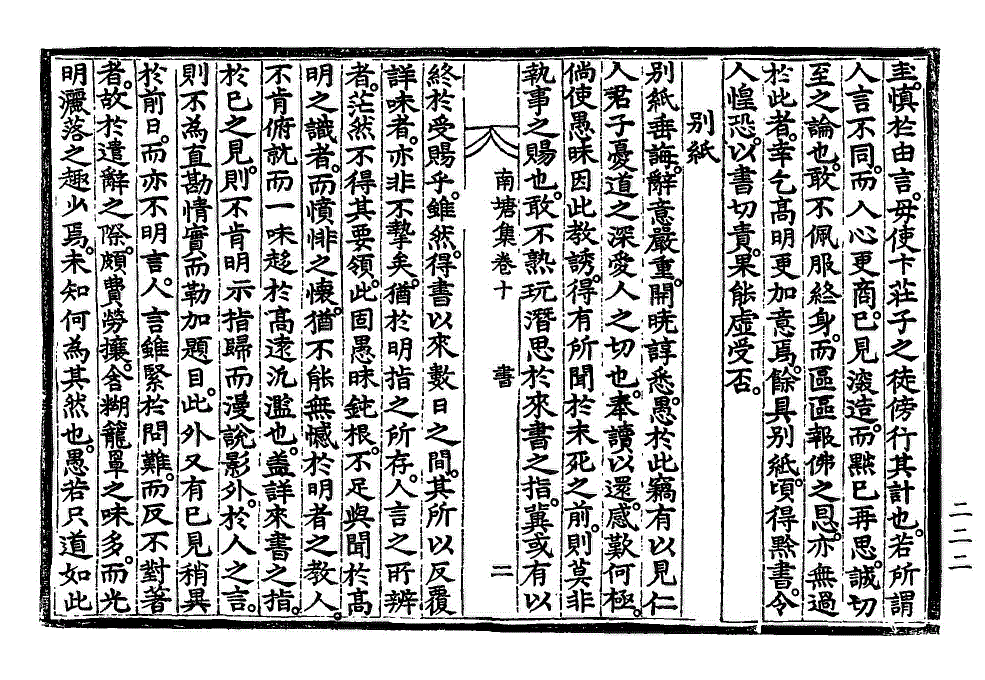 圭。慎于由言。毋使卞庄子之徒傍行其计也。若所谓人言不同。而人心更商。已见深造。而黜己再思。诚切至之论也。敢不佩服终身。而区区报佛之恩。亦无过于此者。幸乞高明更加意焉。馀具别纸。顷得黔书。令人惶恐。以书切责。果能虚受否。
圭。慎于由言。毋使卞庄子之徒傍行其计也。若所谓人言不同。而人心更商。已见深造。而黜己再思。诚切至之论也。敢不佩服终身。而区区报佛之恩。亦无过于此者。幸乞高明更加意焉。馀具别纸。顷得黔书。令人惶恐。以书切责。果能虚受否。别纸
别纸垂诲。辞意严重。开晓谆悉。愚于此窃有以见仁人君子忧道之深爱人之切也。奉读以还。感叹何极。倘使愚昧因此教诱。得有所闻于未死之前。则莫非执事之赐也。敢不熟玩潜思于来书之指。冀或有以终于受赐乎。虽然。得书以来数日之间。其所以反覆详味者。亦非不挚矣。犹于明指之所存。人言之所辨者。茫然不得其要领。此固愚昧钝根。不足与闻于高明之识者。而愤悱之怀。犹不能无憾于明者之教人。不肯俯就而一味趍于高远汎滥也。盖详来书之指。于己之见。则不肯明示指归而漫说影外。于人之言。则不为直勘情实而勒加题目。此外又有己见稍异于前日。而亦不明言。人言虽紧于问难。而反不对著者。故于遣辞之际。颇费劳攘。含糊笼罩之味多。而光明洒落之趣少焉。未知何为其然也。愚若只道如此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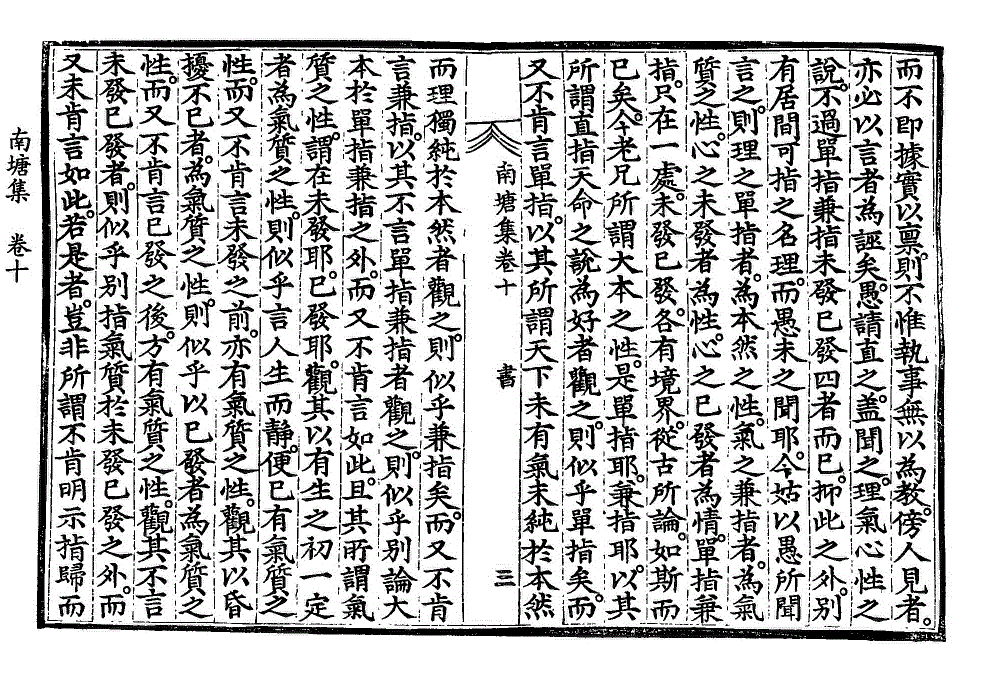 而不即据实以禀。则不惟执事无以为教。傍人见者。亦必以言者为诬矣。愚请直之。盖闻之。理气心性之说。不过单指兼指未发已发四者而已。抑此之外。别有居间可指之名理。而愚未之闻耶。今姑以愚所闻言之。则理之单指者。为本然之性。气之兼指者。为气质之性。心之未发者为性。心之已发者为情。单指兼指。只在一处。未发已发。各有境界。从古所论。如斯而已矣。今老兄所谓大本之性。是单指耶。兼指耶。以其所谓直指天命之说为好者观之。则似乎单指矣。而又不肯言单指。以其所谓天下未有气未纯于本然而理独纯于本然者观之。则似乎兼指矣。而又不肯言兼指。以其不言单指兼指者观之。则似乎别论大本于单指兼指之外。而又不肯言如此。且其所谓气质之性。谓在未发耶。已发耶。观其以有生之初一定者为气质之性。则似乎言人生而静。便已有气质之性。而又不肯言未发之前。亦有气质之性。观其以昏扰不已者。为气质之性。则似乎以已发者为气质之性。而又不肯言已发之后。方有气质之性。观其不言未发已发者。则似乎别指气质于未发已发之外。而又未肯言如此。若是者。岂非所谓不肯明示指归而
而不即据实以禀。则不惟执事无以为教。傍人见者。亦必以言者为诬矣。愚请直之。盖闻之。理气心性之说。不过单指兼指未发已发四者而已。抑此之外。别有居间可指之名理。而愚未之闻耶。今姑以愚所闻言之。则理之单指者。为本然之性。气之兼指者。为气质之性。心之未发者为性。心之已发者为情。单指兼指。只在一处。未发已发。各有境界。从古所论。如斯而已矣。今老兄所谓大本之性。是单指耶。兼指耶。以其所谓直指天命之说为好者观之。则似乎单指矣。而又不肯言单指。以其所谓天下未有气未纯于本然而理独纯于本然者观之。则似乎兼指矣。而又不肯言兼指。以其不言单指兼指者观之。则似乎别论大本于单指兼指之外。而又不肯言如此。且其所谓气质之性。谓在未发耶。已发耶。观其以有生之初一定者为气质之性。则似乎言人生而静。便已有气质之性。而又不肯言未发之前。亦有气质之性。观其以昏扰不已者。为气质之性。则似乎以已发者为气质之性。而又不肯言已发之后。方有气质之性。观其不言未发已发者。则似乎别指气质于未发已发之外。而又未肯言如此。若是者。岂非所谓不肯明示指归而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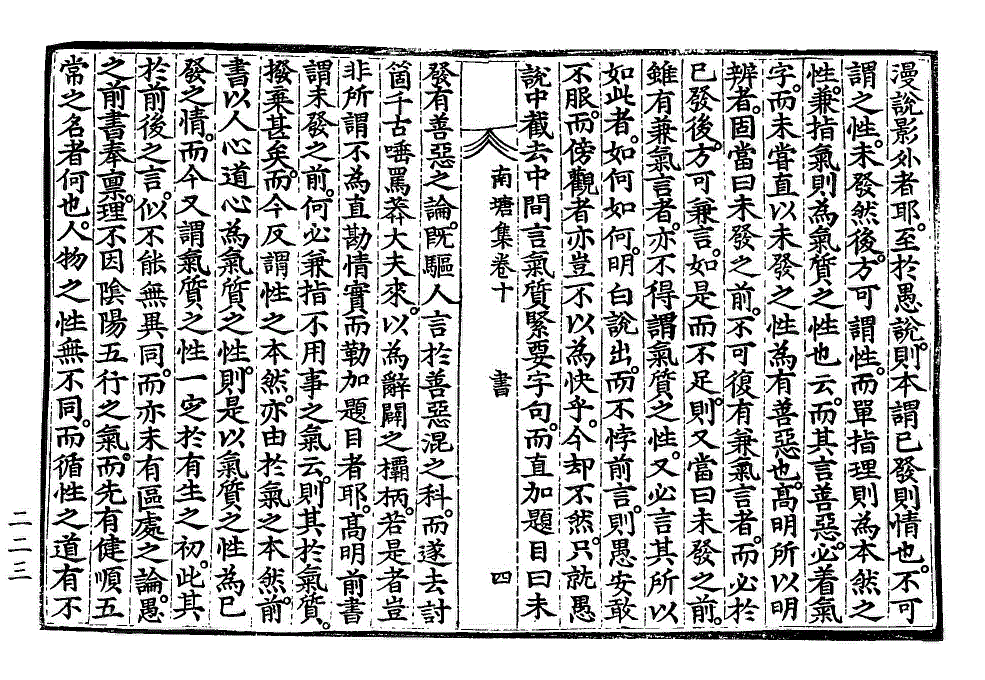 漫说影外者耶。至于愚说。则本谓已发则情也。不可谓之性。未发然后。方可谓性。而单指理则为本然之性。兼指气则为气质之性也云。而其言善恶。必着气字。而未尝直以未发之性为有善恶也。高明所以明辨者。固当曰未发之前。不可复有兼气言者。而必于已发后。方可兼言。如是而不足。则又当曰未发之前。虽有兼气言者。亦不得谓气质之性。又必言其所以如此者。如何如何。明白说出。而不悖前言。则愚安敢不服。而傍观者亦岂不以为快乎。今却不然。只就愚说中截去中间言气质紧要字句。而直加题目曰未发有善恶之论。既驱人言于善恶混之科。而遂去讨个千古唾骂莽大夫来。以为辞辟之𣠽柄。若是者岂非所谓不为直勘情实而勒加题目者耶。高明前书谓未发之前。何必兼指不用事之气云。则其于气质。拨弃甚矣。而今反谓性之本然。亦由于气之本然。前书以人心道心为气质之性。则是以气质之性为已发之情。而今又谓气质之性一定于有生之初。此其于前后之言。似不能无异同。而亦未有区处之论。愚之前书奉禀。理不因阴阳五行之气。而先有健顺五常之名者何也。人物之性无不同。而循性之道有不
漫说影外者耶。至于愚说。则本谓已发则情也。不可谓之性。未发然后。方可谓性。而单指理则为本然之性。兼指气则为气质之性也云。而其言善恶。必着气字。而未尝直以未发之性为有善恶也。高明所以明辨者。固当曰未发之前。不可复有兼气言者。而必于已发后。方可兼言。如是而不足。则又当曰未发之前。虽有兼气言者。亦不得谓气质之性。又必言其所以如此者。如何如何。明白说出。而不悖前言。则愚安敢不服。而傍观者亦岂不以为快乎。今却不然。只就愚说中截去中间言气质紧要字句。而直加题目曰未发有善恶之论。既驱人言于善恶混之科。而遂去讨个千古唾骂莽大夫来。以为辞辟之𣠽柄。若是者岂非所谓不为直勘情实而勒加题目者耶。高明前书谓未发之前。何必兼指不用事之气云。则其于气质。拨弃甚矣。而今反谓性之本然。亦由于气之本然。前书以人心道心为气质之性。则是以气质之性为已发之情。而今又谓气质之性一定于有生之初。此其于前后之言。似不能无异同。而亦未有区处之论。愚之前书奉禀。理不因阴阳五行之气。而先有健顺五常之名者何也。人物之性无不同。而循性之道有不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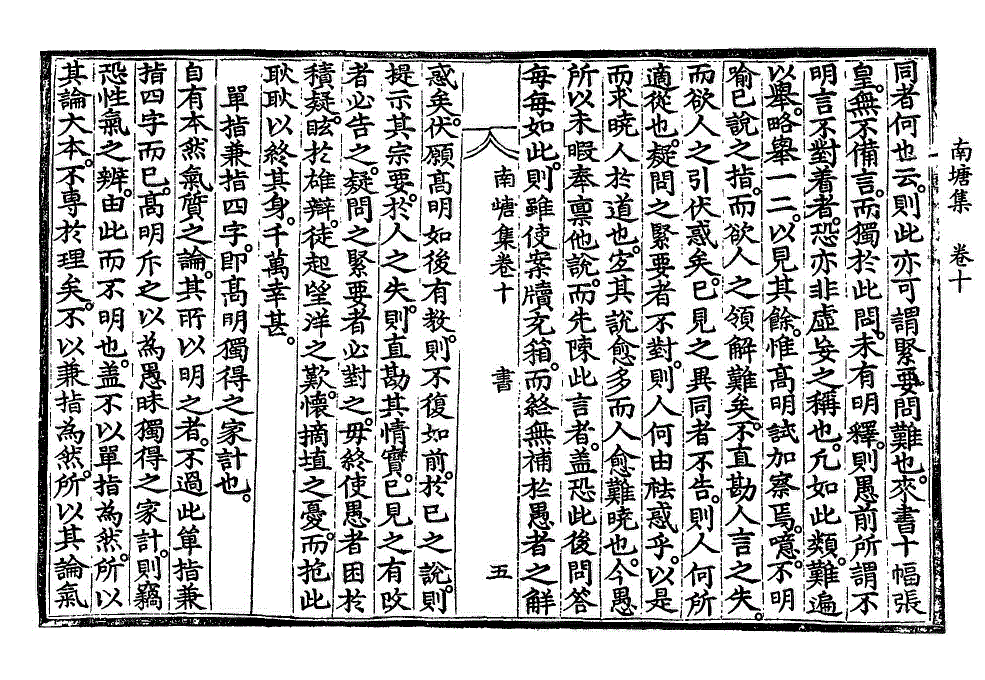 同者何也云。则此亦可谓紧要问难也。来书十幅张皇。无不备言。而独于此问。未有明释。则愚前所谓不明言不对着者。恐亦非虚妄之称也。凡如此类。难遍以举。略举一二。以见其馀。惟高明试加察焉。噫。不明喻己说之指。而欲人之领解难矣。不直勘人言之失。而欲人之引伏惑矣。己见之异同者不告。则人何所适从也。疑问之紧要者不对。则人何由祛惑乎。以是而求晓人于道也。宜其说愈多而人愈难晓也。今愚所以未暇奉禀他说。而先陈此言者。盖恐此后问答每每如此。则虽使案牍充箱。而终无补于愚者之解惑矣。伏愿高明如后有教。则不复如前。于己之说。则提示其宗要。于人之失。则直勘其情实。己见之有改者必告之。疑问之紧要者必对之。毋终使愚者困于积疑。眩于雄辩。徒起望洋之叹。怀摘埴之忧。而抱此耿耿以终其身。千万幸甚。
同者何也云。则此亦可谓紧要问难也。来书十幅张皇。无不备言。而独于此问。未有明释。则愚前所谓不明言不对着者。恐亦非虚妄之称也。凡如此类。难遍以举。略举一二。以见其馀。惟高明试加察焉。噫。不明喻己说之指。而欲人之领解难矣。不直勘人言之失。而欲人之引伏惑矣。己见之异同者不告。则人何所适从也。疑问之紧要者不对。则人何由祛惑乎。以是而求晓人于道也。宜其说愈多而人愈难晓也。今愚所以未暇奉禀他说。而先陈此言者。盖恐此后问答每每如此。则虽使案牍充箱。而终无补于愚者之解惑矣。伏愿高明如后有教。则不复如前。于己之说。则提示其宗要。于人之失。则直勘其情实。己见之有改者必告之。疑问之紧要者必对之。毋终使愚者困于积疑。眩于雄辩。徒起望洋之叹。怀摘埴之忧。而抱此耿耿以终其身。千万幸甚。单指兼指四字。即高明独得之家计也。
自有本然气质之论。其所以明之者。不过此单指兼指四字而已。高明斥之以为愚昧独得之家计。则窃恐性气之辨。由此而不明也。盖不以单指为然。所以其论大本。不专于理矣。不以兼指为然。所以其论气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4L 页
 质。或离于性矣。独得之云。诚不敢当。而家计之责。亦不敢辞。
质。或离于性矣。独得之云。诚不敢当。而家计之责。亦不敢辞。俯笑杨氏以为渠何曾梦到此地。彼朋友以杨氏持我者。率皆抑勒不情之言。而渠何足以知此者也。
杨氏只知有气质之善恶。而不知有本善之性。故其言性。不过气质而已。愚则固已言性之本善。而别论其兼气之有善恶。则本性还他本性。气质还他气质。自不相蒙矣。归杨之罪。诚昏迷不自省也。若愚之所窃惑者。高明方辟杨氏。若是严矣而已。则乃以本然之性和气质而言。则是于气质之外。更无有专言理之性矣。而其论性极致。亦不过气质而已也。以此声罪于杨氏。得无为燕人之伐燕乎。
从古论本然气质者。自程张至栗谷。亦未尝直勘于大本。则直勘之论。自今日发之。
本然者。大本之当体也。气质者。大本之所寓也。本然大本。固非二性。而大本气质。亦非有两地头也。今以本然气质。直勘于大本之地。深斥为无稽。则未知性之为本然者何时。为大本者又何时。而大本在何处。气质又在何处耶。乞指晓之。虽然。愚之论大本。指出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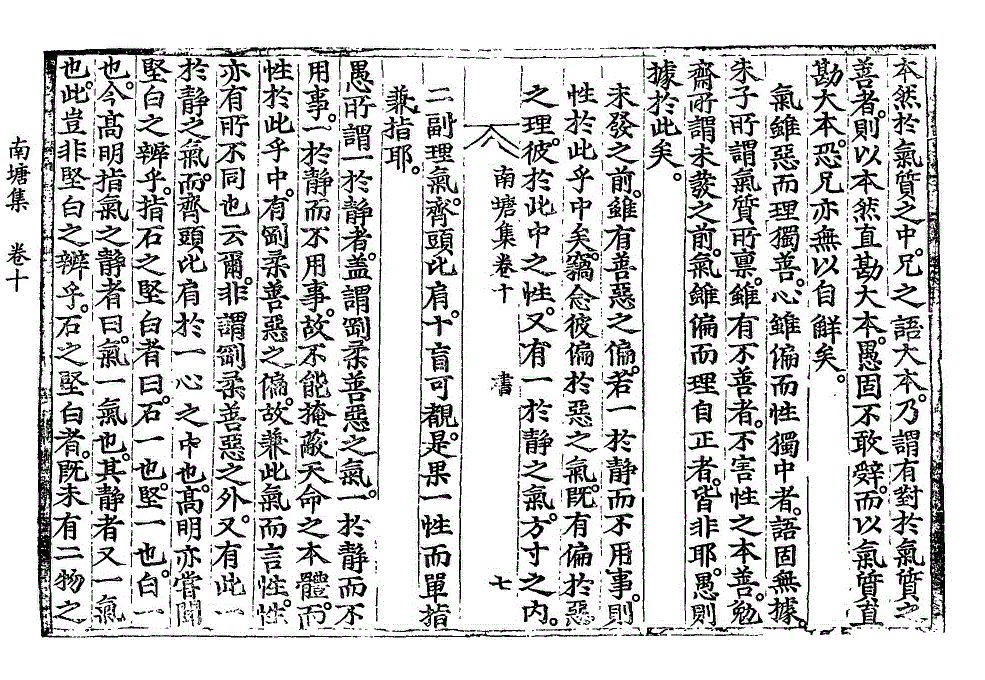 本然于气质之中。兄之语大本。乃谓有对于气质之善者。则以本然直勘大本。愚固不敢辞。而以气质直勘大本。恐兄亦无以自解矣。
本然于气质之中。兄之语大本。乃谓有对于气质之善者。则以本然直勘大本。愚固不敢辞。而以气质直勘大本。恐兄亦无以自解矣。气虽恶而理独善。心虽偏而性独中者。语固无据。
朱子所谓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者。不害性之本善。勉斋所谓未发之前。气虽偏而理自正者。皆非耶。愚则据于此矣。
未发之前。虽有善恶之偏。若一于静而不用事。则性于此乎中矣。窃念彼偏于恶之气。既有偏于恶之理。彼于此中之性。又有一于静之气。方寸之内。二副理气。齐头比肩。十盲可睹。是果一性而单指兼指耶。
愚所谓一于静者。盖谓刚柔善恶之气。一于静而不用事。一于静而不用事。故不能掩蔽天命之本体。而性于此乎中。有刚柔善恶之偏。故兼此气而言性。性亦有所不同也云尔。非谓刚柔善恶之外。又有此一于静之气。而齐头比肩于一心之中也。高明亦尝闻坚白之辨乎。指石之坚白者曰。石一也。坚一也。白一也。今高明指气之静者曰。气一气也。其静者又一气也。此岂非坚白之辨乎。石之坚白者。既未有二物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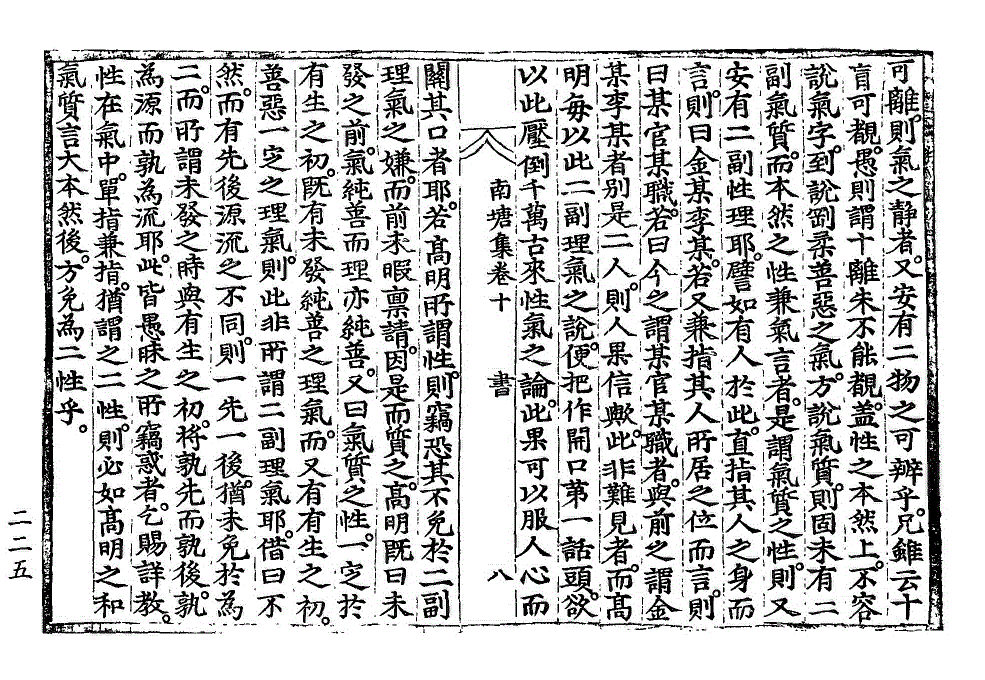 可离。则气之静者。又安有二物之可辨乎。兄虽云十盲可睹。愚则谓十离朱不能睹。盖性之本然上。不容说气字。到说刚柔善恶之气。方说气质。则固未有二副气质。而本然之性兼气言者。是谓气质之性。则又安有二副性理耶。譬如有人于此。直指其人之身而言。则曰金某李某。若又兼指其人所居之位而言。则曰某官某职。若曰今之谓某官某职者。与前之谓金某李某者别是二人。则人果信欤。此非难见者。而高明每以此二副理气之说。便把作开口第一话头。欲以此压倒千万古来性气之论。此果可以服人心而关其口者耶。若高明所谓性。则窃恐其不免于二副理气之嫌。而前未暇禀请。因是而质之。高明既曰未发之前。气纯善而理亦纯善。又曰气质之性。一定于有生之初。既有未发纯善之理气。而又有有生之初。善恶一定之理气。则此非所谓二副理气耶。借曰不然。而有先后源流之不同。则一先一后。犹未免于为二。而所谓未发之时与有生之初。将孰先而孰后。孰为源而孰为流耶。此皆愚昧之所窃惑者。乞赐详教。性在气中。单指兼指。犹谓之二性。则必如高明之和气质言大本然后。方免为二性乎。
可离。则气之静者。又安有二物之可辨乎。兄虽云十盲可睹。愚则谓十离朱不能睹。盖性之本然上。不容说气字。到说刚柔善恶之气。方说气质。则固未有二副气质。而本然之性兼气言者。是谓气质之性。则又安有二副性理耶。譬如有人于此。直指其人之身而言。则曰金某李某。若又兼指其人所居之位而言。则曰某官某职。若曰今之谓某官某职者。与前之谓金某李某者别是二人。则人果信欤。此非难见者。而高明每以此二副理气之说。便把作开口第一话头。欲以此压倒千万古来性气之论。此果可以服人心而关其口者耶。若高明所谓性。则窃恐其不免于二副理气之嫌。而前未暇禀请。因是而质之。高明既曰未发之前。气纯善而理亦纯善。又曰气质之性。一定于有生之初。既有未发纯善之理气。而又有有生之初。善恶一定之理气。则此非所谓二副理气耶。借曰不然。而有先后源流之不同。则一先一后。犹未免于为二。而所谓未发之时与有生之初。将孰先而孰后。孰为源而孰为流耶。此皆愚昧之所窃惑者。乞赐详教。性在气中。单指兼指。犹谓之二性。则必如高明之和气质言大本然后。方免为二性乎。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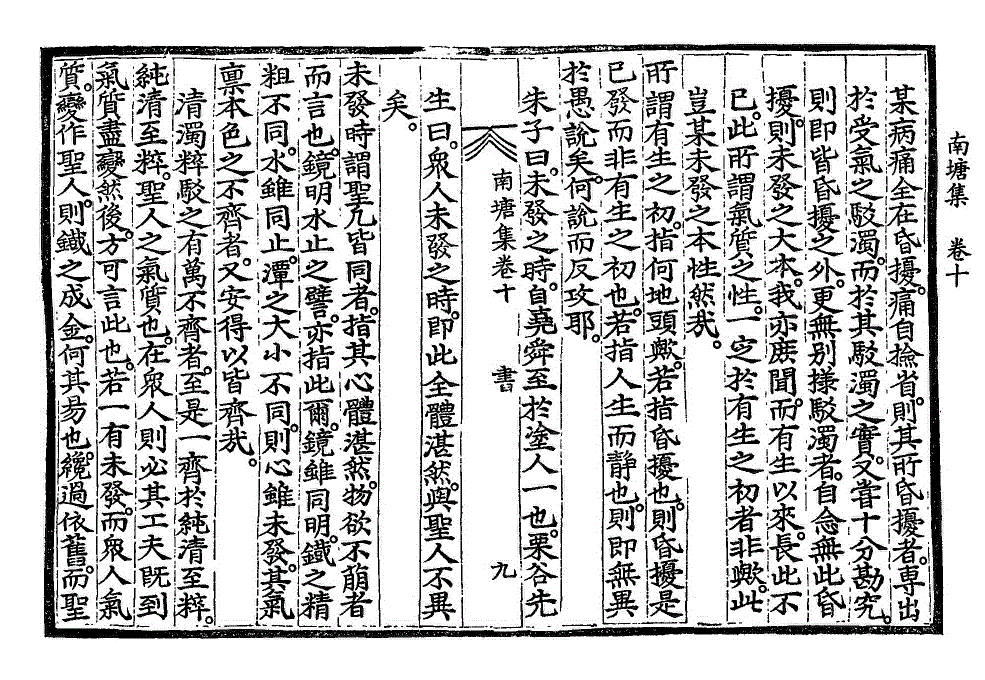 某病痛全在昏扰。痛自检省。则其所昏扰者。专出于受气之驳浊。而于其驳浊之实。又尝十分勘究。则即皆昏扰之外。更无别㨾驳浊者。自念无此昏扰。则未发之大本。我亦庶闻。而有生以来。长此不已。此所谓气质之性。一定于有生之初者非欤。此岂某未发之本性然哉。
某病痛全在昏扰。痛自检省。则其所昏扰者。专出于受气之驳浊。而于其驳浊之实。又尝十分勘究。则即皆昏扰之外。更无别㨾驳浊者。自念无此昏扰。则未发之大本。我亦庶闻。而有生以来。长此不已。此所谓气质之性。一定于有生之初者非欤。此岂某未发之本性然哉。所谓有生之初。指何地头欤。若指昏扰也。则昏扰是已发而非有生之初也。若指人生而静也。则即无异于愚说矣。何说而反攻耶。
朱子曰。未发之时。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栗谷先生曰。众人未发之时。即此全体湛然。与圣人不异矣。
未发时谓圣凡皆同者。指其心体湛然。物欲不萌者而言也。镜明水止之譬。亦指此尔。镜虽同明。铁之精粗不同。水虽同止。潭之大小不同。则心虽未发。其气禀本色之不齐者。又安得以皆齐哉。
清浊粹驳之有万不齐者。至是一齐于纯清至粹。
纯清至粹。圣人之气质也。在众人则必其工夫既到气质尽变然后。方可言此也。若一有未发。而众人气质。变作圣人。则铁之成金。何其易也。才过依旧。而圣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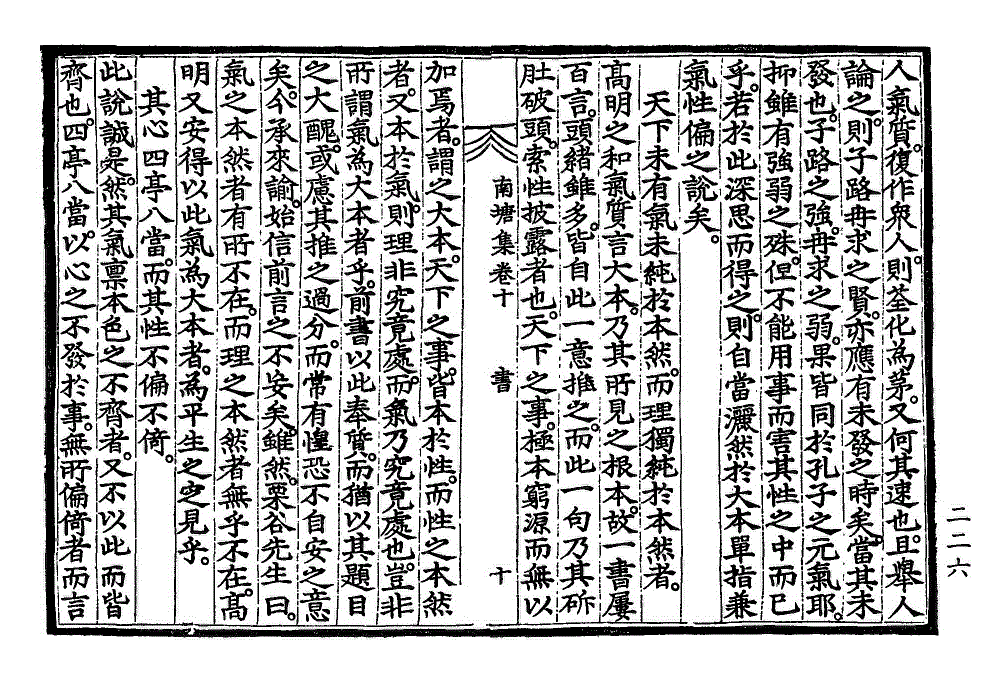 人气质。复作众人。则荃化为茅。又何其速也。且举人论之。则子路冉求之贤。亦应有未发之时矣。当其未发也。子路之强。冉求之弱。果皆同于孔子之元气耶。抑虽有强弱之殊。但不能用事而害其性之中而已乎。若于此深思而得之。则自当洒然于大本单指兼气性偏之说矣。
人气质。复作众人。则荃化为茅。又何其速也。且举人论之。则子路冉求之贤。亦应有未发之时矣。当其未发也。子路之强。冉求之弱。果皆同于孔子之元气耶。抑虽有强弱之殊。但不能用事而害其性之中而已乎。若于此深思而得之。则自当洒然于大本单指兼气性偏之说矣。天下未有气未纯于本然。而理独纯于本然者。
高明之和气质言大本。乃其所见之根本。故一书屡百言。头绪虽多。皆自此一意推之。而此一句乃其斫肚破头。索性披露者也。天下之事。极本穷源而无以加焉者。谓之大本。天下之事。皆本于性。而性之本然者。又本于气。则理非究竟处。而气乃究竟处也。岂非所谓气为大本者乎。前书以此奉质。而犹以其题目之大丑。或虑其推之过分。而常有惶恐不自安之意矣。今承来谕。始信前言之不妄矣。虽然。栗谷先生曰。气之本然者有所不在。而理之本然者无乎不在。高明又安得以此气为大本者。为平生之定见乎。
其心四亭八当。而其性不偏不倚。
此说诚是。然其气禀本色之不齐者。又不以此而皆齐也。四亭八当。以心之不发于事。无所偏倚者而言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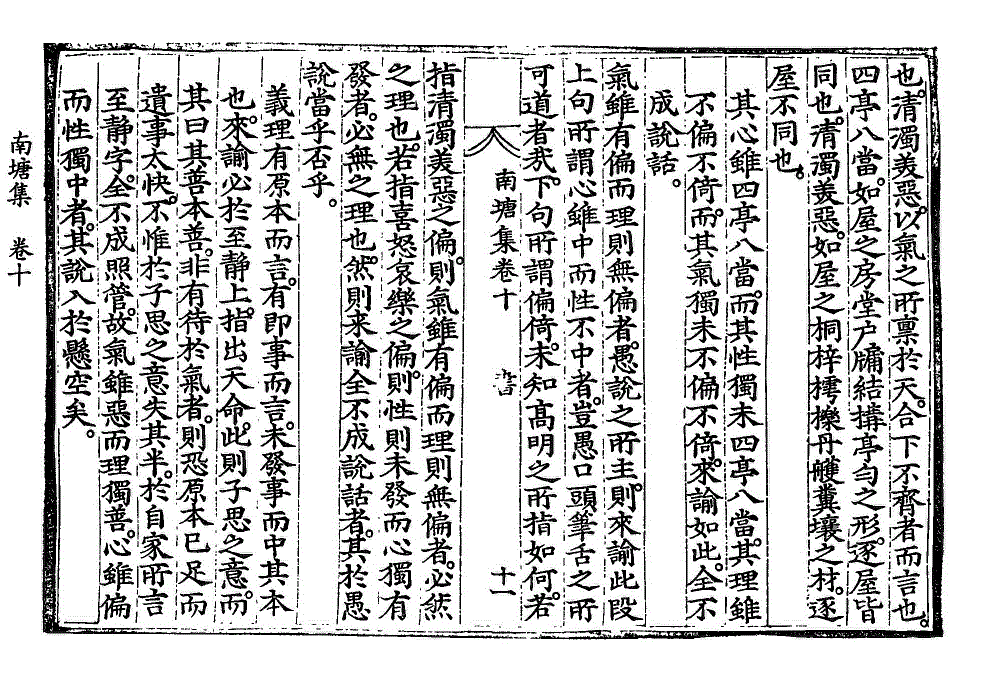 也。清浊美恶。以气之所禀于天。合下不齐者而言也。四亭八当。如屋之房堂户牖结搆亭匀之形。逐屋皆同也。清浊美恶。如屋之桐梓樗栎丹艧粪壤之材。逐屋不同也。
也。清浊美恶。以气之所禀于天。合下不齐者而言也。四亭八当。如屋之房堂户牖结搆亭匀之形。逐屋皆同也。清浊美恶。如屋之桐梓樗栎丹艧粪壤之材。逐屋不同也。其心虽四亭八当。而其性独未四亭八当。其理虽不偏不倚。而其气独未不偏不倚。来谕如此。全不成说话。
气虽有偏而理则无偏者。愚说之所主。则来谕此段上句所谓心虽中而性不中者。岂愚口头笔舌之所可道者哉。下句所谓偏倚。未知高明之所指如何。若指清浊美恶之偏。则气虽有偏而理则无偏者。必然之理也。若指喜怒哀乐之偏。则性则未发而心独有发者。必无之理也。然则来谕全不成说话者。其于愚说当乎否乎。
义理有原本而言。有即事而言。未发事而中其本也。来谕必于至静上。指出天命。此则子思之意。而其曰其善本善。非有待于气者。则恐原本已足而遗事太快。不惟于子思之意失其半。于自家所言至静字。全不成照管。故气虽恶而理独善。心虽偏而性独中者。其说入于悬空矣。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7L 页
 即事原本之论甚善。然在愚说则可矣。而在高明说则恐不免为倒戈之卒矣。即乎至静则所谓即事也。直指天命而不杂乎气则所谓原本也。高明亦曰即乎至静。则所谓即事者然矣。而必曰天命之善。有待于气质。则所谓原本者。谓之原本于气则可矣。而谓之原本于性则非矣。夫中之必即乎至静而单指此理者何也。盖才出乎静。则即是已发也。已发则情也。不可谓之性也。已发则偏倚矣。不可谓之中也。此所以必即乎静而言者也。至静之中。气不用事。则湛然虚明。虽未有善恶之形焉。既有此气。则亦不能无本色美恶之相杂。而若兼此气而言性。则无以见其性之善矣。此所以必单指理而言者也。自非圣以下。虽于至静之中。而气禀本色。固必有美恶之相杂。然设使至此而气一齐皆善。若性之善。则决不待于此矣。性而待于气善。则岂非所谓气质之性也。岂非所谓气为之大本乎。若然则孟子当言气善而不当言性善也。本善之性。未发而中。则中与善一矣。何失乎子思之意也。何反乎自家之言静也。未发之中。又必待气质而善。则中与善二矣。性与善二矣。其不失于子思之意乎。亦不反于自家之言本善乎。气虽恶。理独
即事原本之论甚善。然在愚说则可矣。而在高明说则恐不免为倒戈之卒矣。即乎至静则所谓即事也。直指天命而不杂乎气则所谓原本也。高明亦曰即乎至静。则所谓即事者然矣。而必曰天命之善。有待于气质。则所谓原本者。谓之原本于气则可矣。而谓之原本于性则非矣。夫中之必即乎至静而单指此理者何也。盖才出乎静。则即是已发也。已发则情也。不可谓之性也。已发则偏倚矣。不可谓之中也。此所以必即乎静而言者也。至静之中。气不用事。则湛然虚明。虽未有善恶之形焉。既有此气。则亦不能无本色美恶之相杂。而若兼此气而言性。则无以见其性之善矣。此所以必单指理而言者也。自非圣以下。虽于至静之中。而气禀本色。固必有美恶之相杂。然设使至此而气一齐皆善。若性之善。则决不待于此矣。性而待于气善。则岂非所谓气质之性也。岂非所谓气为之大本乎。若然则孟子当言气善而不当言性善也。本善之性。未发而中。则中与善一矣。何失乎子思之意也。何反乎自家之言静也。未发之中。又必待气质而善。则中与善二矣。性与善二矣。其不失于子思之意乎。亦不反于自家之言本善乎。气虽恶。理独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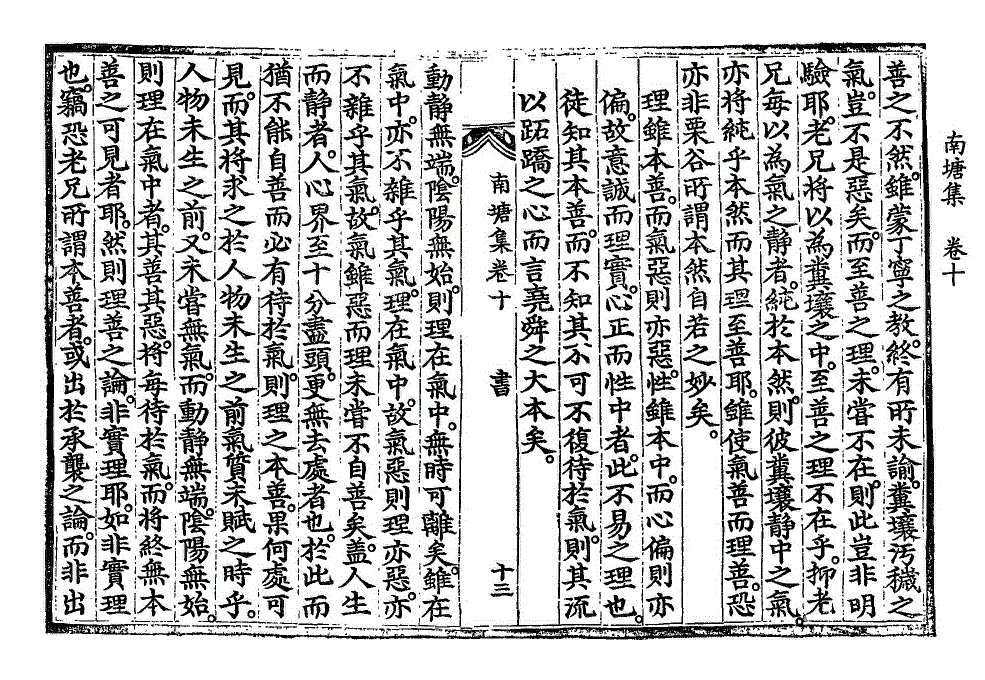 善之不然。虽蒙丁宁之教。终有所未谕。粪壤污秽之气。岂不是恶矣。而至善之理。未尝不在。则此岂非明验耶。老兄将以为粪壤之中。至善之理不在乎。抑老兄每以为气之静者。纯于本然。则彼粪壤静中之气。亦将纯乎本然而其理至善耶。虽使气善而理善。恐亦非栗谷所谓本然自若之妙矣。
善之不然。虽蒙丁宁之教。终有所未谕。粪壤污秽之气。岂不是恶矣。而至善之理。未尝不在。则此岂非明验耶。老兄将以为粪壤之中。至善之理不在乎。抑老兄每以为气之静者。纯于本然。则彼粪壤静中之气。亦将纯乎本然而其理至善耶。虽使气善而理善。恐亦非栗谷所谓本然自若之妙矣。理虽本善。而气恶则亦恶。性虽本中。而心偏则亦偏。故意诚而理实。心正而性中者。此不易之理也。徒知其本善。而不知其不可不复待于气。则其流以蹠蹻之心而言尧舜之大本矣。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在气中。无时可离矣。虽在气中。亦不杂乎其气。理在气中。故气恶则理亦恶。亦不杂乎其气。故气虽恶而理未尝不自善矣。盖人生而静者。人心界至十分尽头。更无去处者也。于此而犹不能自善而必有待于气。则理之本善。果何处可见。而其将求之于人物未生之前气质未赋之时乎。人物未生之前。又未尝无气。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在气中者。其善其恶。将每待于气。而将终无本善之可见者耶。然则理善之论。非实理耶。如非实理也。窃恐老兄所谓本善者。或出于承袭之论。而非出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8L 页
 于实见者耶。蹠蹻之气质。非尧舜之气质。而蹠蹻之性。即尧舜之性。则性善之不待于气。即来谕而可见矣。但蹠蹻之心。无一刻未发。故性不能中而大本不立矣。若以其无未发也。无气质之些儿善也。而遂谓之无大本无性善也。则不亦误乎。(性则大本。而中则大本之立也。)虽然。以来谕气恶则理恶气善则理善者观之。则未发之前。未尝无气质。而未尝不兼言者。又昭昭矣。何执事乐言乎彼而恶闻乎此也。盖高明初怕其大本之或染于气质之恶者。则遽欲离其不可离之气质。及其终不可离。则又去讨个气质之善者。以为安顿大本之所。而自不觉其既兼气质则便有善恶。而不免于挽大本而堕善恶之混矣。此其理势然也。苟深察乎性气不离不杂之妙。则岂有如是之患哉。
于实见者耶。蹠蹻之气质。非尧舜之气质。而蹠蹻之性。即尧舜之性。则性善之不待于气。即来谕而可见矣。但蹠蹻之心。无一刻未发。故性不能中而大本不立矣。若以其无未发也。无气质之些儿善也。而遂谓之无大本无性善也。则不亦误乎。(性则大本。而中则大本之立也。)虽然。以来谕气恶则理恶气善则理善者观之。则未发之前。未尝无气质。而未尝不兼言者。又昭昭矣。何执事乐言乎彼而恶闻乎此也。盖高明初怕其大本之或染于气质之恶者。则遽欲离其不可离之气质。及其终不可离。则又去讨个气质之善者。以为安顿大本之所。而自不觉其既兼气质则便有善恶。而不免于挽大本而堕善恶之混矣。此其理势然也。苟深察乎性气不离不杂之妙。则岂有如是之患哉。乐言乎天命而不知在至静。乐言乎大本而不知在未发。则其谬已甚。
愚之言天命大本。未尝不在至静。抑老兄认至静之气为纯善。而愚谓有善恶故云然耶。若然则自阴阳五行以下。至于万物。而其阴一半则皆善。而阳又有善。则善常占三分地耶。然则天下之善人常少而小人常多。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何也。是未可知也。愚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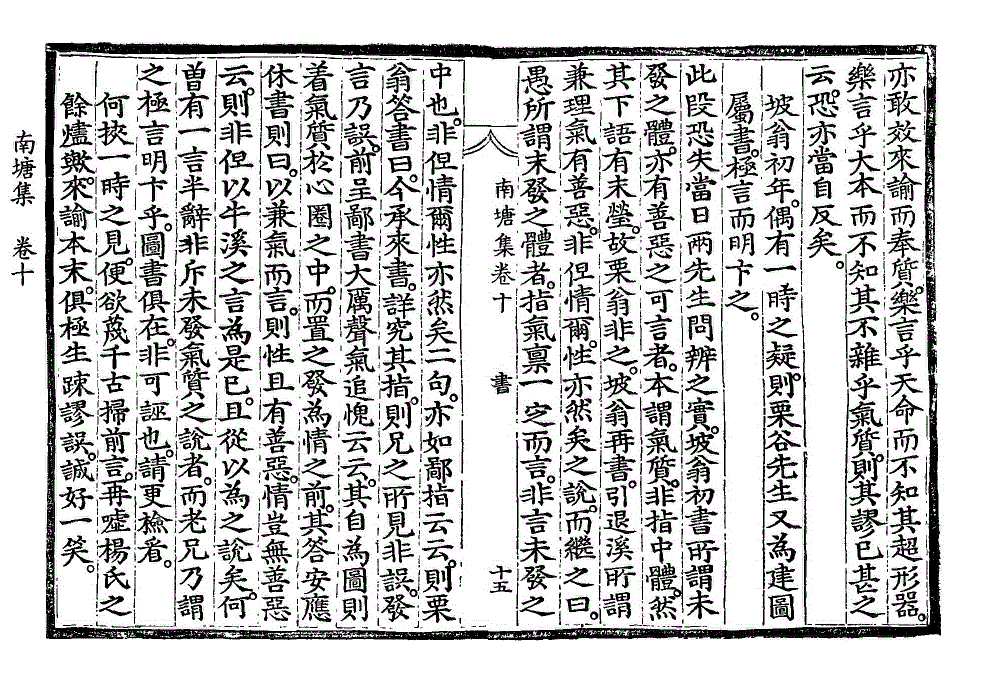 亦敢效来谕而奉质。乐言乎天命而不知其超形器。乐言乎大本而不知其不杂乎气质。则其谬已甚之云。恐亦当自反矣。
亦敢效来谕而奉质。乐言乎天命而不知其超形器。乐言乎大本而不知其不杂乎气质。则其谬已甚之云。恐亦当自反矣。坡翁初年。偶有一时之疑。则栗谷先生又为建图属书。极言而明卞之。
此段恐失当日两先生问辨之实。坡翁初书所谓未发之体。亦有善恶之可言者。本谓气质。非指中体。然其下语有未莹。故栗翁非之。坡翁再书。引退溪所谓兼理气有善恶。非但情尔。性亦然矣之说。而继之曰。愚所谓未发之体者。指气禀一定而言。非言未发之中也。非但情尔性亦然矣二句。亦如鄙指云云。则栗翁答书曰。今承来书。详究其指。则兄之所见非误。发言乃误。前呈鄙书大厉声气追愧云云。其自为图则着气质于心圈之中。而置之发为情之前。其答安应休书则曰。以兼气而言。则性且有善恶。情岂无善恶云。则非但以牛溪之言为是已。且从以为之说矣。何曾有一言半辞非斥未发气质之说者。而老兄乃谓之极言明卞乎。图书俱在。非可诬也。请更检看。
何挟一时之见。便欲蔑千古扫前言。再嘘杨氏之馀烬欤。来谕本末。俱极生疏谬误。诚好一笑。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9L 页
 杨氏之所以为杨氏者。不过认气质为性而已。今高明之说根极领要处。亦不过认气质为大本。则其不同于杨氏者何事。抑杨氏善恶俱认。而高明只认其善。此其为不同耶。虽然。才说气质必有善恶。则高明所谓善者里面。恐不免包藏凶恶。而反不如杨氏之直道善恶。为朴实头为学也。然则杨氏之馀烬再嘘者谁也。自是看非。固宜好笑。但己见未必尽是。人见未必尽非。则安知不有庐山之外。复有人好笑耶。
杨氏之所以为杨氏者。不过认气质为性而已。今高明之说根极领要处。亦不过认气质为大本。则其不同于杨氏者何事。抑杨氏善恶俱认。而高明只认其善。此其为不同耶。虽然。才说气质必有善恶。则高明所谓善者里面。恐不免包藏凶恶。而反不如杨氏之直道善恶。为朴实头为学也。然则杨氏之馀烬再嘘者谁也。自是看非。固宜好笑。但己见未必尽是。人见未必尽非。则安知不有庐山之外。复有人好笑耶。毕竟函丈之地。亦不免为所动。区区于此窃深不幸。兄则所造虽已高明。而世视以后生。且自家进德之程。如日方升。安知今虽偶失而后终于不得也。即今函丈非义精仁熟道成德尊之日乎。名理一出。四方学者视为定论。而偶然被误于后生不思之论。晚年大本。却从杨氏之说。则其为吾党之不幸也。为如何哉。此区区寤言独叹。不觉明发而不寐者也。
末端所谕。老兄于此乎未免失言矣。惜乎。子贡所谓驷不及舌者。不幸而近之也。岂兄以函丈初可于兄问。而复印于愚说者而云然耶。此尽有曲折。当初高明举鄙说。禀于函丈。不言气质字。而直谓某为未发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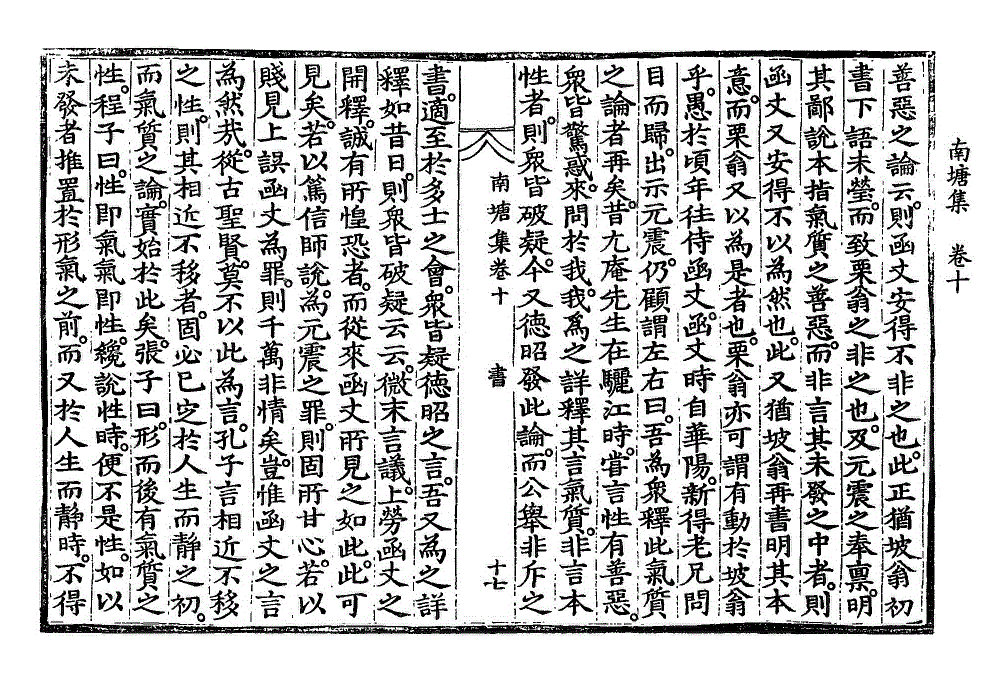 善恶之论云。则函丈安得不非之也。此正犹坡翁初书下语未莹。而致栗翁之非之也。及元震之奉禀。明其鄙说本指气质之善恶。而非言其未发之中者。则函丈又安得不以为然也。此又犹坡翁再书明其本意。而栗翁又以为是者也。栗翁亦可谓有动于坡翁乎。愚于顷年往侍函丈。函丈时自华阳。新得老兄问目而归。出示元震。仍顾谓左右曰。吾为众释此气质之论者再矣。昔尤庵先生在骊江时。尝言性有善恶。众皆惊惑。来问于我。我为之详释其言气质。非言本性者。则众皆破疑。今又德昭发此论。而公举非斥之书。适至于多士之会。众皆疑德昭之言。吾又为之详释如昔日。则众皆破疑云云。微末言议。上劳函丈之开释。诚有所惶恐者。而从来函丈所见之如此。此可见矣。若以笃信师说。为元震之罪。则固所甘心。若以贱见上误函丈为罪。则千万非情矣。岂惟函丈之言为然哉。从古圣贤。莫不以此为言。孔子言相近不移之性。则其相近不移者。固必已定于人生而静之初。而气质之论。实始于此矣。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程子曰。性即气气即性。才说性时。便不是性。如以未发者推置于形气之前。而又于人生而静时。不得
善恶之论云。则函丈安得不非之也。此正犹坡翁初书下语未莹。而致栗翁之非之也。及元震之奉禀。明其鄙说本指气质之善恶。而非言其未发之中者。则函丈又安得不以为然也。此又犹坡翁再书明其本意。而栗翁又以为是者也。栗翁亦可谓有动于坡翁乎。愚于顷年往侍函丈。函丈时自华阳。新得老兄问目而归。出示元震。仍顾谓左右曰。吾为众释此气质之论者再矣。昔尤庵先生在骊江时。尝言性有善恶。众皆惊惑。来问于我。我为之详释其言气质。非言本性者。则众皆破疑。今又德昭发此论。而公举非斥之书。适至于多士之会。众皆疑德昭之言。吾又为之详释如昔日。则众皆破疑云云。微末言议。上劳函丈之开释。诚有所惶恐者。而从来函丈所见之如此。此可见矣。若以笃信师说。为元震之罪。则固所甘心。若以贱见上误函丈为罪。则千万非情矣。岂惟函丈之言为然哉。从古圣贤。莫不以此为言。孔子言相近不移之性。则其相近不移者。固必已定于人生而静之初。而气质之论。实始于此矣。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程子曰。性即气气即性。才说性时。便不是性。如以未发者推置于形气之前。而又于人生而静时。不得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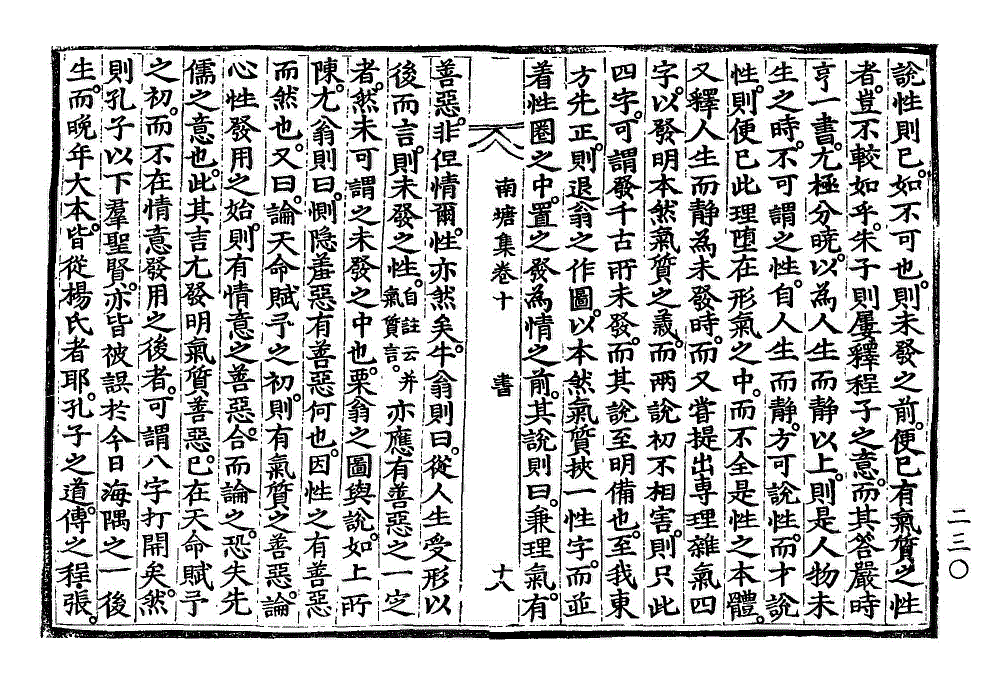 说性则已。如不可也。则未发之前。便已有气质之性者。岂不较如乎。朱子则屡释程子之意。而其答严时亨一书。尤极分晓。以为人生而静以上。则是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之性。自人生而静。方可说性。而才说性。则便已此理堕在形气之中。而不全是性之本体。又释人生而静为未发时。而又尝提出专理杂气四字。以发明本然气质之义。而两说初不相害。则只此四字。可谓发千古所未发。而其说至明备也。至我东方先正。则退翁之作图。以本然气质挟一性字。而并着性圈之中。置之发为情之前。其说则曰。兼理气。有善恶。非但情尔。性亦然矣。牛翁则曰。从人生受形以后而言。则未发之性。(自注云并气质言。)亦应有善恶之一定者。然未可谓之未发之中也。栗翁之图与说。如上所陈。尤翁则曰。恻隐羞恶有善恶何也。因性之有善恶而然也。又曰。论天命赋予之初。则有气质之善恶。论心性发用之始。则有情意之善恶。合而论之。恐失先儒之意也。此其言尤发明气质善恶。已在天命赋予之初。而不在情意发用之后者。可谓八字打开矣。然则孔子以下群圣贤。亦皆被误于今日海隅之一后生。而晚年大本。皆从杨氏者耶。孔子之道。传之程,张。
说性则已。如不可也。则未发之前。便已有气质之性者。岂不较如乎。朱子则屡释程子之意。而其答严时亨一书。尤极分晓。以为人生而静以上。则是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之性。自人生而静。方可说性。而才说性。则便已此理堕在形气之中。而不全是性之本体。又释人生而静为未发时。而又尝提出专理杂气四字。以发明本然气质之义。而两说初不相害。则只此四字。可谓发千古所未发。而其说至明备也。至我东方先正。则退翁之作图。以本然气质挟一性字。而并着性圈之中。置之发为情之前。其说则曰。兼理气。有善恶。非但情尔。性亦然矣。牛翁则曰。从人生受形以后而言。则未发之性。(自注云并气质言。)亦应有善恶之一定者。然未可谓之未发之中也。栗翁之图与说。如上所陈。尤翁则曰。恻隐羞恶有善恶何也。因性之有善恶而然也。又曰。论天命赋予之初。则有气质之善恶。论心性发用之始。则有情意之善恶。合而论之。恐失先儒之意也。此其言尤发明气质善恶。已在天命赋予之初。而不在情意发用之后者。可谓八字打开矣。然则孔子以下群圣贤。亦皆被误于今日海隅之一后生。而晚年大本。皆从杨氏者耶。孔子之道。传之程,张。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1H 页
 程,张之道。传之朱子。朱子之道。传之退,栗。沙溪亲学于栗谷。尤翁亲学于沙溪。而我先生又亲学于尤翁。则的传相承。渊源甚远。顾此议论。虽系气质之粗末。若不识此。必有累于大本。则其于讲明授受之际。亦岂视以第二等义而不为明覈其实乎。况其言议著在方策者。前后一揆。若合符节。而炳如日星之中天。则此岂以一后生孤单之见。所可容易立说破也。然则来谕所谓挟一时不思之见。蔑千古扫前言者。亦愿高明之自省也。噫。高明之论。到底以杨氏为口实。然归善恶于气质。论大本于指出者。幸无悖于孔子以来群圣贤之指。则顾何损于勒加之题目。而混大本于气质。气必兼乎善恶。则若是者未必非杨氏所俟后世之子云也。寤言独叹。明发不寐者。何独在高明而然也。
程,张之道。传之朱子。朱子之道。传之退,栗。沙溪亲学于栗谷。尤翁亲学于沙溪。而我先生又亲学于尤翁。则的传相承。渊源甚远。顾此议论。虽系气质之粗末。若不识此。必有累于大本。则其于讲明授受之际。亦岂视以第二等义而不为明覈其实乎。况其言议著在方策者。前后一揆。若合符节。而炳如日星之中天。则此岂以一后生孤单之见。所可容易立说破也。然则来谕所谓挟一时不思之见。蔑千古扫前言者。亦愿高明之自省也。噫。高明之论。到底以杨氏为口实。然归善恶于气质。论大本于指出者。幸无悖于孔子以来群圣贤之指。则顾何损于勒加之题目。而混大本于气质。气必兼乎善恶。则若是者未必非杨氏所俟后世之子云也。寤言独叹。明发不寐者。何独在高明而然也。愚既就来书所谕。逐段供对。以禀其疑。请复得以通论之。今日所争论说虽多。要其归趣则不过两端而已。老兄以为未发之前。不可兼言气。而谓有气质之性。愚则以为可兼言气。而谓有气质之性。老兄以为性之本然。必有待于气质。不可遗气而语大本。愚则以为性本善。非有待于气质。不可和气质而论大本。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1L 页
 即此两端而究覈得之。则是非不难定矣。盖无极二五。本浑融而无间。不以动静而有异也。若于未发之前。不可复兼气而言。则此未发之气。将无其所以然之理。而理外有气。气外有理。不复相干矣。乌有其浑融无间乎。理气虽本浑融。而亦不相杂。理则纯善。而气则不纯。若不因其不杂者而指出此理单言之。则又无以见其性之本善。而大本或沦于善恶之混矣。此其未发之前。虽有兼气言者。而至于大本。决不可一毫混气而言也。愚请以水在器中烛在房中者譬之。水在器中者。逐器方圆。其形不同矣。而其静也未尝离于器之匡郭矣。烛在房中者。无风牵动。其焰正中矣。而其光也无所待于室之明暗矣。若谓水之静者离于器。而烛之明者待于室。则不亦误乎。又窃怪老兄于大本则不惮以气言之。而至于言气质之性。则必深攻之。又不觉其大本之待气者。便即是气质之性。而不免自作元只。何其然也。愚见如是。有不然者。愿闻高明之详释也。
即此两端而究覈得之。则是非不难定矣。盖无极二五。本浑融而无间。不以动静而有异也。若于未发之前。不可复兼气而言。则此未发之气。将无其所以然之理。而理外有气。气外有理。不复相干矣。乌有其浑融无间乎。理气虽本浑融。而亦不相杂。理则纯善。而气则不纯。若不因其不杂者而指出此理单言之。则又无以见其性之本善。而大本或沦于善恶之混矣。此其未发之前。虽有兼气言者。而至于大本。决不可一毫混气而言也。愚请以水在器中烛在房中者譬之。水在器中者。逐器方圆。其形不同矣。而其静也未尝离于器之匡郭矣。烛在房中者。无风牵动。其焰正中矣。而其光也无所待于室之明暗矣。若谓水之静者离于器。而烛之明者待于室。则不亦误乎。又窃怪老兄于大本则不惮以气言之。而至于言气质之性。则必深攻之。又不觉其大本之待气者。便即是气质之性。而不免自作元只。何其然也。愚见如是。有不然者。愿闻高明之详释也。单指兼指未发已发之说。前已发之。请申禀焉。老兄所谓大本之性。若是兼指也。则自古性善之论。未有兼气言者矣。若是单指也。则其善又何待于气。而必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2H 页
 谓之有待耶。彼兼气言性者。别是一义。则其说又何妨于此。而必欲其不言乎。老兄所谓气质之性。谓在未发也。则与愚见无异矣。谓在已发也。则是本然之性。发为气质之性。而一前一后。分明有二性何也。先贤之每以气质之性对情言者亦何也。抑以为不单指不兼指。而别有所指大本之性。不在未发不在已发。而别有所具气质之性也。则前言未尝有如此者何也。天下之义理。虽云无穷。老兄之言性。即必居一于此矣。愿闻指一之教。此外又有所禀。性之乘气质。即太极之乘阴阳也。太极之乘阴静者。兼言之而为阴静之性。则性之乘气质之静者。独不可兼言者何也。枯槁之物。一味至静。而亦皆兼言理气。谓有气质之性。则人心之至静者。独不可兼言理气者何也。毋曰烦猥而一一俯答幸甚。
谓之有待耶。彼兼气言性者。别是一义。则其说又何妨于此。而必欲其不言乎。老兄所谓气质之性。谓在未发也。则与愚见无异矣。谓在已发也。则是本然之性。发为气质之性。而一前一后。分明有二性何也。先贤之每以气质之性对情言者亦何也。抑以为不单指不兼指。而别有所指大本之性。不在未发不在已发。而别有所具气质之性也。则前言未尝有如此者何也。天下之义理。虽云无穷。老兄之言性。即必居一于此矣。愿闻指一之教。此外又有所禀。性之乘气质。即太极之乘阴阳也。太极之乘阴静者。兼言之而为阴静之性。则性之乘气质之静者。独不可兼言者何也。枯槁之物。一味至静。而亦皆兼言理气。谓有气质之性。则人心之至静者。独不可兼言理气者何也。毋曰烦猥而一一俯答幸甚。五常说。来谕辞说尤繁。纵横错互。无甚条理。不可端倪。然细究其指。则所主有二。五常可言于一原。而不可言于异体也。五常本然。可以超形气言。而不可因气质言也。所證有二。中庸首章之注也。大学或问之语也。所攻有二。谓天命五常之判为二物也。谓五常之认为气质也。即此六者而定其是非。则馀可定矣。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2L 页
 谨具禀于下。
谨具禀于下。一原异体
一原者。一而无二之称也。异体者。二而不一之谓也。一而无二。故一原上。不可更着多一字。二而不一。故异体者自二。以下皆是。而不待有万而后然也。是故太极之无加无对者。为一原理同。自是而分为阴阳五行。则是为异体。而理之为健顺五常者。为理不同矣。阴阳五行。既为异体理不同。则其在万物者。又可知矣。今指健顺之二五常之五而谓之一原。则其为一原也。何其不一之甚也。且自太极。以至阴阳五行。同为一原。则一原分数。又何其多也。二与五数之可见者。屈指数之。不难知也。而犹谓之一。则殆有甚于孙子荆之洗耳砺齿。公孙龙之藏三耳也。人安得开口争之。一原未莹。异体亦未莹者。来谕正是也。
五常超形气
太极之理。乘阴阳则为健顺之德。乘五行则为五常之德。自有健顺五常之名目。便已如此说矣。今曰超形气而有五常。则是健顺具于无阴阳之地。五常立于无五行之地矣。其言性也。不亦悬空驾虚之甚乎。盖健顺五常。即气质而指本然者也。即气质而言。故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3H 页
 有健顺五常之殊。(太极图解曰五性之殊。)而不得为一原矣。指本然而言。故为纯粹至善之德。而不失为本然矣。苟察乎此。则何疑乎即气质而为本然。为本然而不得为一原者乎。不因阴阳五行之气而先有健顺五常之名者。前书奉禀其疑。而略不开释。愚者何以解惑乎。更乞毋惜回谕。(直指本然不因乎气质。则所谓一原者。又未尝外乎此性矣。)
有健顺五常之殊。(太极图解曰五性之殊。)而不得为一原矣。指本然而言。故为纯粹至善之德。而不失为本然矣。苟察乎此。则何疑乎即气质而为本然。为本然而不得为一原者乎。不因阴阳五行之气而先有健顺五常之名者。前书奉禀其疑。而略不开释。愚者何以解惑乎。更乞毋惜回谕。(直指本然不因乎气质。则所谓一原者。又未尝外乎此性矣。)中庸首章注
此注当为性异之證。而不当为性同之案。愚与彦明书中详释之。想必登照。此不复详。略举其概而奉质焉。性与道。同乎异乎。以为异则非敢知。以为同则人物之道异矣。性安得同乎。所得之性所循之性。同耶异耶。以为异则非敢知。以为同则所循者异矣。所得者安得同乎。抑以为人能率性而物不能率性欤。则章句所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者。又何谓也。前书有禀。未蒙开释。老兄所据。既在于此。则不问当谕。况于有问乎。乞赐明教。
大学或问说
或问曰。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上下文文义义例。不应有异同。老兄既据上句以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3L 页
 为物之得是理者。皆得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则亦将据下句以为物之得是气者。无论通塞。皆具魂魄五脏百骸之身乎。此盖言仁义礼智之性得于理。五脏百骸之身得于气云尔。岂谓物之得此理气者。一切皆具仁义礼智五脏百骸云乎。成仲书中。已释此意。而老兄既不敢为非。亦未有他释。而只得依前作證而已。则此岂讲论之道乎。前贤言性不同则必言五常。言五常则必言禀不同。如此言者。虽连纸百幅。不可尽录。而老兄于此。既皆一笔句断。驱之于气质善恶之性。虽以老兄之淹贯经籍。终不得检出一言明白可證己说者。而艰难去寻庸注或问略可牵合底此二段来。以为据依枝拄之𣠽柄。而终无奈我欲同而彼自异。则未知老兄又失于此。更从何处转其身耶。窃叹窃叹。
为物之得是理者。皆得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则亦将据下句以为物之得是气者。无论通塞。皆具魂魄五脏百骸之身乎。此盖言仁义礼智之性得于理。五脏百骸之身得于气云尔。岂谓物之得此理气者。一切皆具仁义礼智五脏百骸云乎。成仲书中。已释此意。而老兄既不敢为非。亦未有他释。而只得依前作證而已。则此岂讲论之道乎。前贤言性不同则必言五常。言五常则必言禀不同。如此言者。虽连纸百幅。不可尽录。而老兄于此。既皆一笔句断。驱之于气质善恶之性。虽以老兄之淹贯经籍。终不得检出一言明白可證己说者。而艰难去寻庸注或问略可牵合底此二段来。以为据依枝拄之𣠽柄。而终无奈我欲同而彼自异。则未知老兄又失于此。更从何处转其身耶。窃叹窃叹。天命五常判为二物
天命。通天下万事万物而无不可说。五常。于木谓仁。于金谓义。指一处一事而言。通天下言者。岂非超形器者也。指一处一事言者。岂非因气质者乎。天命五常。其辨只如此而已。岂谓天命不为五常。而五常不原天命乎。老兄既谓无辨。则愚请还问左右。天命可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4H 页
 以偏指一事。而五常可以互换名实乎。如以为可则愚何说。如以为不可。则又何斥乎愚说也。愚之此论。盖亦泛论天命五常尔。非就中庸首章首句而言也。若就此而论之。则所谓天命之性者。主乎人而兼乎物者也。在人则莫非全体矣。物则堇得其形气之偏者。而不能有以通贯乎天命之全体。然天命之全体。又未尝外乎其所得之偏者矣。自其所赋之气偏而所赋之理亦偏者而言之。则谓之性命俱偏可也。自其天命全体不外乎其所得者而言之。则谓之性命俱全可也。(此则掉了形气。单指天命而言。)自其天命流行一般而物之所受不同者而言之。则谓之命全而性偏亦可也。以此而言。愚亦何曾谓子思之论。只在于异体而不及于一原哉。
以偏指一事。而五常可以互换名实乎。如以为可则愚何说。如以为不可。则又何斥乎愚说也。愚之此论。盖亦泛论天命五常尔。非就中庸首章首句而言也。若就此而论之。则所谓天命之性者。主乎人而兼乎物者也。在人则莫非全体矣。物则堇得其形气之偏者。而不能有以通贯乎天命之全体。然天命之全体。又未尝外乎其所得之偏者矣。自其所赋之气偏而所赋之理亦偏者而言之。则谓之性命俱偏可也。自其天命全体不外乎其所得者而言之。则谓之性命俱全可也。(此则掉了形气。单指天命而言。)自其天命流行一般而物之所受不同者而言之。则谓之命全而性偏亦可也。以此而言。愚亦何曾谓子思之论。只在于异体而不及于一原哉。五常认为气质
健顺五常之立名。本因于阴阳五行之气矣。若以其因气质得名。而便斥为气质之性。则当初命名。亦本以气质善恶之性而言耶。抑即气质指本然而言者耶。若如老兄之言。而超阴阳五行而说健顺五常。则其为清脱则至矣。而其奈为健为顺为五常。俱无所因而入于玄空何哉。来谕本然而不得为一原何欤。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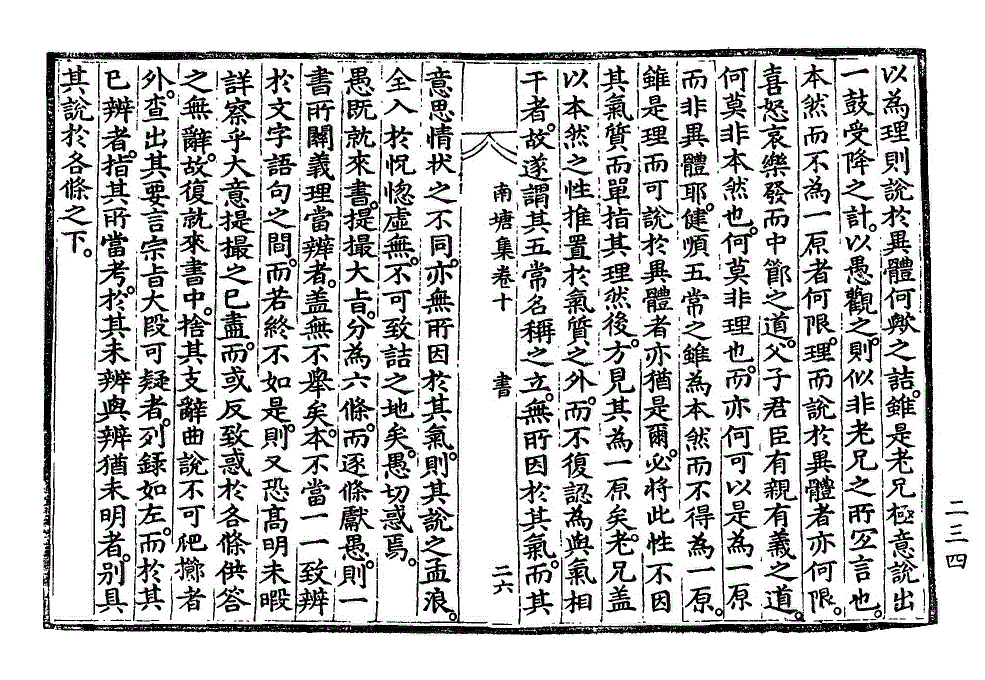 以为理则说于异体何欤之诘。虽是老兄极意说出一鼓受降之计。以愚观之。则似非老兄之所宜言也。本然而不为一原者何限。理而说于异体者亦何限。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之道。父子君臣有亲有义之道。何莫非本然也。何莫非理也。而亦何可以是为一原而非异体耶。健顺五常之虽为本然而不得为一原。虽是理而可说于异体者亦犹是尔。必将此性不因其气质而单指其理然后。方见其为一原矣。老兄盖以本然之性推置于气质之外。而不复认为与气相干者。故遂谓其五常名称之立。无所因于其气。而其意思情状之不同。亦无所因于其气。则其说之孟浪。全入于恍惚虚无。不可致诘之地矣。愚切惑焉。
以为理则说于异体何欤之诘。虽是老兄极意说出一鼓受降之计。以愚观之。则似非老兄之所宜言也。本然而不为一原者何限。理而说于异体者亦何限。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之道。父子君臣有亲有义之道。何莫非本然也。何莫非理也。而亦何可以是为一原而非异体耶。健顺五常之虽为本然而不得为一原。虽是理而可说于异体者亦犹是尔。必将此性不因其气质而单指其理然后。方见其为一原矣。老兄盖以本然之性推置于气质之外。而不复认为与气相干者。故遂谓其五常名称之立。无所因于其气。而其意思情状之不同。亦无所因于其气。则其说之孟浪。全入于恍惚虚无。不可致诘之地矣。愚切惑焉。愚既就来书。提撮大旨。分为六条。而逐条献愚。则一书所关义理当辨者。盖无不举矣。本不当一一致辨于文字语句之间。而若终不如是。则又恐高明未暇详察乎大意提撮之已尽。而或反致惑于各条供答之无辞。故复就来书中。舍其支辞曲说不可爬栉者外。查出其要言宗旨大段可疑者。列录如左。而于其已辨者。指其所当考。于其未辨与辨犹未明者。别具其说于各条之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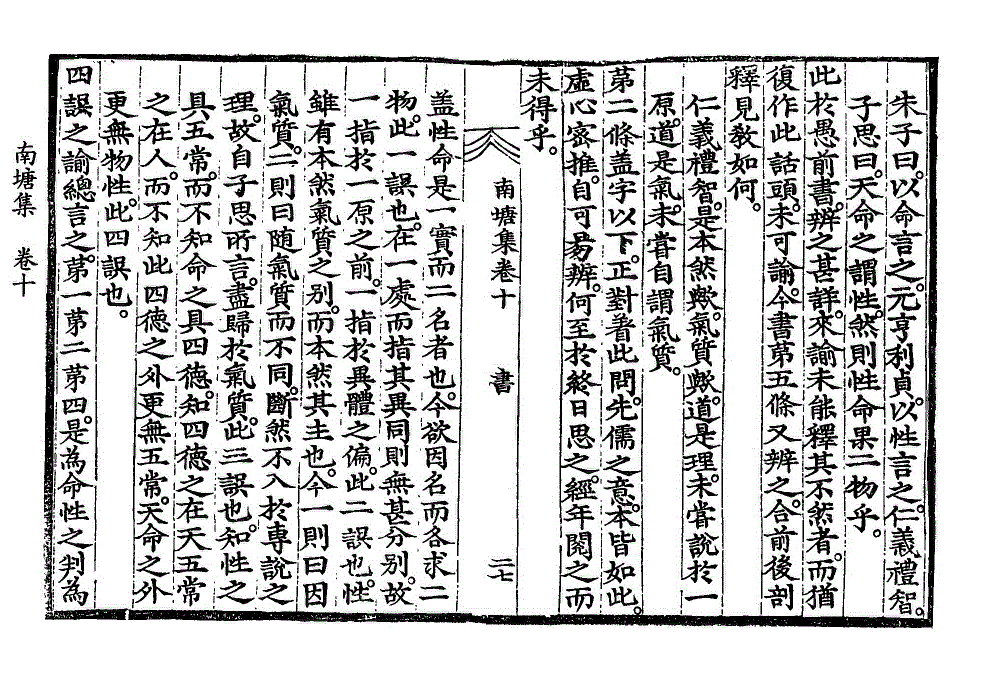 朱子曰。以命言之。元亨利贞。以性言之。仁义礼智。子思曰。天命之谓性。然则性命果二物乎。
朱子曰。以命言之。元亨利贞。以性言之。仁义礼智。子思曰。天命之谓性。然则性命果二物乎。此于愚前书。辨之甚详。来谕未能释其不然者。而犹复作此话头。未可谕。今书第五条又辨之。合前后剖释见教如何。
仁义礼智。是本然欤。气质欤。道是理。未尝说于一原。道是气。未尝自谓气质。
第二条盖字以下。正对着此问。先儒之意。本皆如此。虚心密推。自可易辨。何至于终日思之。经年阅之而未得乎。
盖性命是一实而二名者也。今欲因名而各求二物。此一误也。在一处而指其异同则无甚分别。故一指于一原之前。一指于异体之偏。此二误也。性虽有本然气质之别。而本然其主也。今一则曰因气质。二则曰随气质而不同。断然不入于专说之理。故自子思所言。尽归于气质。此三误也。知性之具五常。而不知命之具四德。知四德之在天五常之在人。而不知此四德之外更无五常。天命之外更无物性。此四误也。
四误之谕总言之。第一第二第四。是为命性之判为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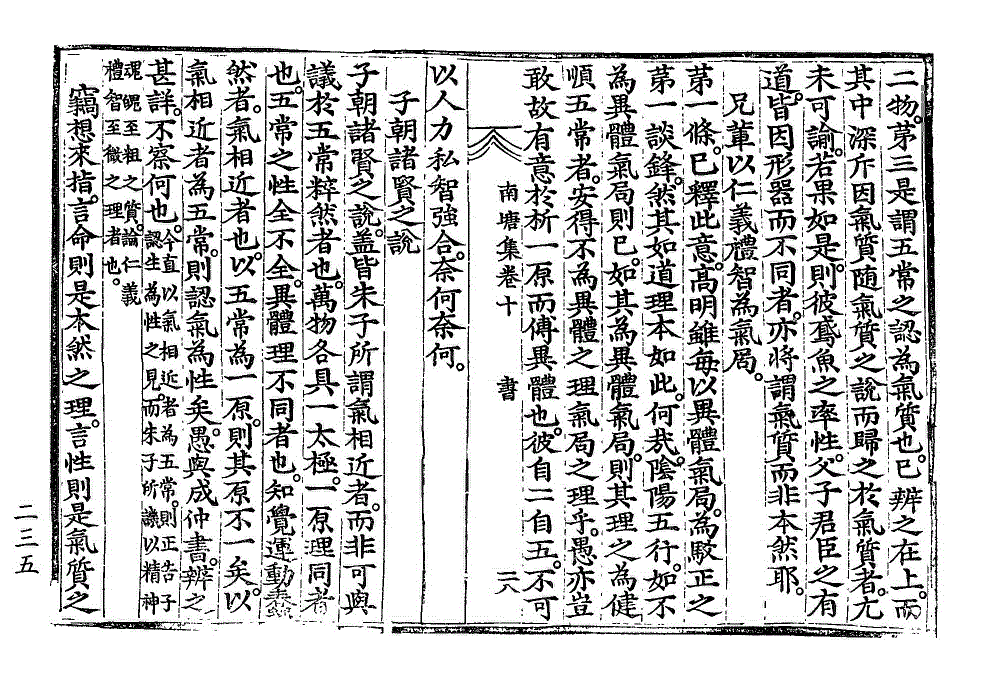 二物。第三是谓五常之认为气质也。已辨之在上。而其中深斥因气质随气质之说而归之于气质者。尤未可谕。若果如是。则彼鸢鱼之率性。父子君臣之有道。皆因形器而不同者。亦将谓气质而非本然耶。
二物。第三是谓五常之认为气质也。已辨之在上。而其中深斥因气质随气质之说而归之于气质者。尤未可谕。若果如是。则彼鸢鱼之率性。父子君臣之有道。皆因形器而不同者。亦将谓气质而非本然耶。兄辈以仁义礼智为气局。
第一条。已释此意。高明虽每以异体气局。为驳正之第一谈锋。然其如道理本如此。何哉。阴阳五行。如不为异体气局则已。如其为异体气局。则其理之为健顺五常者。安得不为异体之理气局之理乎。愚亦岂敢故有意于析一原而傅异体也。彼自二自五。不可以人力私智强合。奈何奈何。
子朝诸贤之说
子朝诸贤之说。盖皆朱子所谓气相近者。而非可与议于五常粹然者也。万物各具一太极。一原理同者也。五常之性全不全。异体理不同者也。知觉运动蠢然者。气相近者也。以五常为一原。则其原不一矣。以气相近者为五常。则认气为性矣。愚与成仲书。辨之甚详。不察何也。(今直以气相近者为五常。则正告子认生为性之见。而朱子所讥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质。论仁义礼智至微之理者也。)
窃想来指。言命则是本然之理。言性则是气质之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6H 页
 性。所言虽多。纲领在是。
性。所言虽多。纲领在是。言性则是气质。非愚说之纲领。即阴阳五行之气。直指健顺五常之理。而谓之本然之性。以理之滚杂乎气者。而谓之气质之性者。愚说之纲领也。超阴阳五行之气。自立健顺五常之名。而谓之本然之性。以理之因气质名者。而谓之气质之性者。高论之纲领也。纲领不同。宜其下稍无一同也。
子思所言性者。即异体而指其一原不杂乎异体者而言。故于本然气质人物率性之道。水临万壑。
来谕所谓即异体而指一原者。指赋予一般之命则可。而指禀受不同之性则不可。指舍气专言之太极则可。而指因气异禀之五常则不可。然其实则一而已矣。但其所就而言之者不同。故有不容浑沦而无辨也。又其所谓人物所率之性。是指本然也。则老兄所谓本然者。即人物皆同之谓也。率此人物皆同之性。而却为人物不同之道何也。若是指气质也。则所得者本然。而所率者气质何也。既率气质。则必有善恶。而通谓之道。亦何也。然则来谕所谓水临万壑者。无乃为过颡在山者耶。愚意人物之性。所得之全者。亦本然也。所得之偏者。亦本然也。(鸢鱼之性。虽偏于飞跃。亦莫非本然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6L 页
 也。)循其性之全而为道之全者。亦本然也。循其性之偏而为道之偏者。亦本然也。(中庸或问。以形气所得之偏。为天命本然。)所谓异体中本然也。方其在性也。单言太极之本体。及其为道也。单言太极之流行。则又莫非全体也。所谓一原上本然也。如此言之。方见其为体用一原之妙。而庶几乎其水临万壑者乎。(异体二字。所该甚广包。本然气质善恶偏全而言。)
也。)循其性之全而为道之全者。亦本然也。循其性之偏而为道之偏者。亦本然也。(中庸或问。以形气所得之偏。为天命本然。)所谓异体中本然也。方其在性也。单言太极之本体。及其为道也。单言太极之流行。则又莫非全体也。所谓一原上本然也。如此言之。方见其为体用一原之妙。而庶几乎其水临万壑者乎。(异体二字。所该甚广包。本然气质善恶偏全而言。)五常若是气。而论于异体。则此当无说。若是理。则天地万物。同此一原矣。
五常之当言于异体。前固已辨之。若来谕之说异体则只可言气。而不可复言理。理则只可言于一原。而不可复言于异体者。其判理气为二物。甚矣。从来所见之误。恐在于此矣。
鄙见则天命五常太极本然。初非有彼此本末偏全大小之异也。
太极天命五常本然。虽是一物。所指不同。故天命太极。全而不偏。五常偏而不全。本然或以全言。或以偏言。不可如来谕之鹘突儱侗看也。来谕所谓五常之全者。指一事而皆谓之全耶。抑合五者而方谓之全耶。若指一事而谓全。则仁外不当复有义之事。义外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7H 页
 不当复有仁之事。而当初言性者。亦当只言一事。不当复言其他矣。若是合五者而谓之全。则是虽以来书之辨。亦不能掩一事之为偏矣。五常自体。已自各偏。则得是以为性者。又安得皆全也。大抵天命太极。专以不杂者而言也。气质善恶之性。专以不离者而言也。健顺五常。兼不杂不离之意而言也。盖即异体而指本然者也。如是看破。自无如来谕之鹘突儱侗者矣。
不当复有仁之事。而当初言性者。亦当只言一事。不当复言其他矣。若是合五者而谓之全。则是虽以来书之辨。亦不能掩一事之为偏矣。五常自体。已自各偏。则得是以为性者。又安得皆全也。大抵天命太极。专以不杂者而言也。气质善恶之性。专以不离者而言也。健顺五常。兼不杂不离之意而言也。盖即异体而指本然者也。如是看破。自无如来谕之鹘突儱侗者矣。反以彼一原为细分。则其说益紊矣。
愚前书所谓细分者。以万物之气相近处理相近者为言。而兄反以此为一原。则兄之一原。亦不过相近而已。非所谓理同者矣。前以阴阳五行为一原。而今又以万物之气相近者为一原。则兄之一原。何其丛杂零琐而头绪之太多耶。兄言至此。愚复何说。
毕竟五常。是理欤非欤。以为理则说于异体者何欤。是理之粹然者。故人独有五常。则其必以粹然者说于异体。而又必以昏浊者说于一原者何欤。然则五常贵而天命贱欤。从古圣贤之说。有片言半辞可證者欤。前人而有此言。则其不得为圣贤决矣。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7L 页
 异体之说。前屡言之。即气质而言之。故五常之粹然者。于人独全。超形器而言之。故天命之本然者。无物不全。非有贵贱善恶之辨者也。孟子辑注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是则以五常言于异体也。栗谷先生曰。粪壤污秽之中。理无不在。而其本然之妙。不害其自若也。是则以一原言于昏浊也。然则两先生之为此言。亦同归于乱道误人。而不得为圣贤欤。何言之易也。
异体之说。前屡言之。即气质而言之。故五常之粹然者。于人独全。超形器而言之。故天命之本然者。无物不全。非有贵贱善恶之辨者也。孟子辑注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是则以五常言于异体也。栗谷先生曰。粪壤污秽之中。理无不在。而其本然之妙。不害其自若也。是则以一原言于昏浊也。然则两先生之为此言。亦同归于乱道误人。而不得为圣贤欤。何言之易也。论其气质。则非惟犬之性非牛之性也。蹠之性。非舜之性矣。语其本然。则不惟蹠之性即舜之性也。物之性。即人之性矣。
同则舜蹠人物皆同。而其同也同。异则舜蹠人物皆异。而其异也亦同。则人物之间相去。仅如舜蹠之间耶。然则同胞异类之言诬矣。
若以仁义礼智。为气质之性。而别指本然于天命太极而曰。言性处不可以理易之。言理处不可以性释之。则非鄙见所及。
愚未尝以仁义礼智。为气质之性。而别指天命太极本然于此德之外也。言性处固可以理易之。言理处亦可以性释之。然以性理二字。并举对言。则理同而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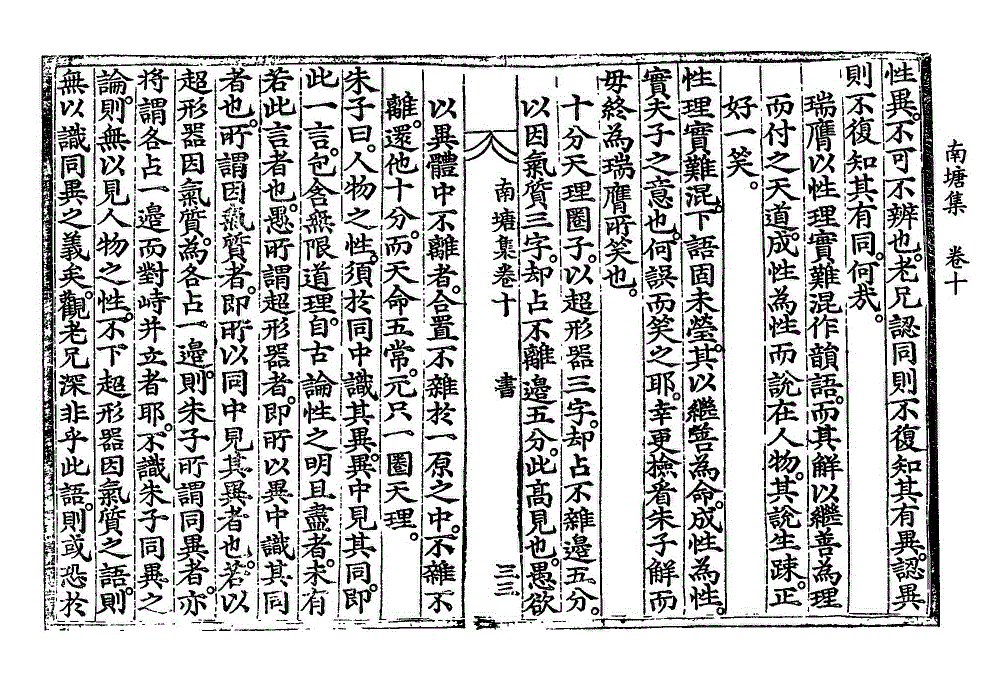 性异。不可不辨也。老兄认同则不复知其有异。认异则不复知其有同。何哉。
性异。不可不辨也。老兄认同则不复知其有异。认异则不复知其有同。何哉。瑞膺以性理实难混作韵语。而其解以继善为理而付之天道。成性为性而说在人物。其说生疏。正好一笑。
性理实难混。下语固未莹。其以继善为命。成性为性。实夫子之意也。何误而笑之耶。幸更检看朱子解而毋终为瑞膺所笑也。
十分天理圈子。以超形器三字。却占不杂边五分。以因气质三字。却占不离边五分。此高见也。愚欲以异体中不离者。合置不杂于一原之中。不杂不离。还他十分。而天命五常。元只一圈天理。
朱子曰。人物之性。须于同中识其异。异中见其同。即此一言。包含无限道理。自古论性之明且尽者。未有若此言者也。愚所谓超形器者。即所以异中识其同者也。所谓因气质者。即所以同中见其异者也。若以超形器因气质。为各占一边。则朱子所谓同异者。亦将谓各占一边而对峙并立者耶。不识朱子同异之论。则无以见人物之性。不下超形器因气质之语。则无以识同异之义矣。观老兄深非乎此语。则或恐于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8L 页
 朱子之言。未识其趣。而所以不辨人物之性者。正在此乎。不杂不离。本非二物。而今欲合置则已不审矣。况其超阴阳五行而说健顺五常者。其于一原不杂者。既失之矣。(谓之五则非一矣。)而于异体不离者。又绝不近矣。(谓之超气则非不离者矣。)然则所谓合置者。果合之于何时。而置之于何地欤。区区于此窃所未谕。
朱子之言。未识其趣。而所以不辨人物之性者。正在此乎。不杂不离。本非二物。而今欲合置则已不审矣。况其超阴阳五行而说健顺五常者。其于一原不杂者。既失之矣。(谓之五则非一矣。)而于异体不离者。又绝不近矣。(谓之超气则非不离者矣。)然则所谓合置者。果合之于何时。而置之于何地欤。区区于此窃所未谕。大抵兄辈俱为不杂不离理气分合等语所误。转辗失真。
来书于鄙说之所误。论辨既备矣。而卒乃指其被误之根本。使有所省而有改焉。则盛意勤笃。何敢昧也。虽然。愚迷之见。终不觉其被误于此语。而反疑明者之为其不欲被误者所误尔。请略言之。性与气质不可离也。而高明深辟未发气质之说。性与气质又不可杂也。而高明反谓性之本然。本于气质。阴阳五行之外。决无健顺五常之德。而高明超是气而语是德。性在气中。不害其为本然。而高明认因气(朱子曰。凡言性。皆因气质而言。)而为气质。此恐于不杂不离之妙。俱有所未察也。惟其不察乎不离者。故于其不可分者。或分之。惟其不察乎不杂者。故于其不可合者。或合之。本领如此。馀可知矣。噫。从古圣贤发明理气之妙者。不过此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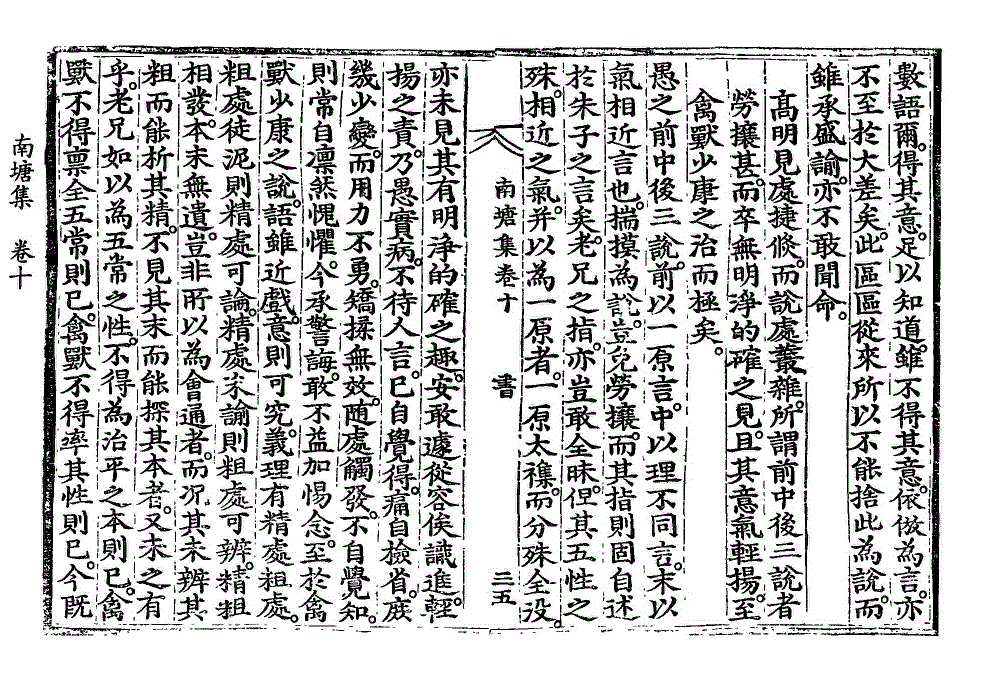 数语尔。得其意。足以知道。虽不得其意。依仿为言。亦不至于大差矣。此区区从来所以不能舍此为说。而虽承盛谕。亦不敢闻命。
数语尔。得其意。足以知道。虽不得其意。依仿为言。亦不至于大差矣。此区区从来所以不能舍此为说。而虽承盛谕。亦不敢闻命。高明见处捷倏。而说处丛杂。所谓前中后三说者劳攘甚。而卒无明净的确之见。且其意气轻扬。至禽兽少康之治而极矣。
愚之前中后三说。前以一原言。中以理不同言。末以气相近言也。揣摸为说。岂免劳攘。而其指则固自述于朱子之言矣。老兄之指。亦岂敢全昧。但其五性之殊。相近之气。并以为一原者。一原太杂。而分殊全没。亦未见其有明净的确之趣。安敢遽从容俟识进。轻扬之责。乃愚实病。不待人言。已自觉得。痛自检省。庶几少变。而用力不勇。矫揉无效。随处触发。不自觉知。则常自凛然愧惧。今承警诲。敢不益加惕念。至于禽兽少康之说。语虽近戏。意则可究。义理有精处粗处。粗处徒泥则精处可论。精处未谕则粗处可辨。精粗相发。本末无遗。岂非所以为会通者。而况其未辨其粗而能析其精。不见其末而能探其本者。又未之有乎。老兄如以为五常之性。不得为治平之本则已。禽兽不得禀全五常则已。禽兽不得率其性则已。今既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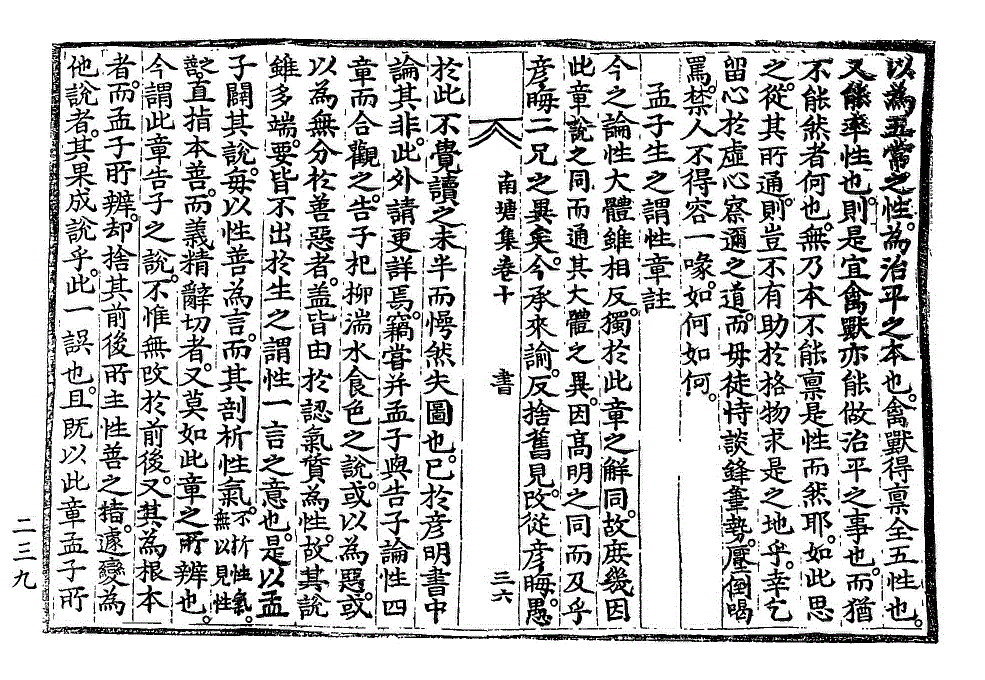 以为五常之性。为治平之本也。禽兽得禀全五性也。又能率性也。则是宜禽兽亦能做治平之事也。而犹不能然者何也。无乃本不能禀是性而然耶。如此思之。从其所通。则岂不有助于格物求是之地乎。幸乞留心于虚心察迩之道。而毋徒恃谈锋笔势。压倒喝骂。禁人不得容一喙。如何如何。
以为五常之性。为治平之本也。禽兽得禀全五性也。又能率性也。则是宜禽兽亦能做治平之事也。而犹不能然者何也。无乃本不能禀是性而然耶。如此思之。从其所通。则岂不有助于格物求是之地乎。幸乞留心于虚心察迩之道。而毋徒恃谈锋笔势。压倒喝骂。禁人不得容一喙。如何如何。孟子生之谓性章注
今之论性大体虽相反。独于此章之解同。故庶几因此章说之同而通其大体之异。因高明之同而及乎彦,晦二兄之异矣。今承来谕。反舍旧见。改从彦,晦。愚于此不觉读之未半而愕然失图也。已于彦明书中论其非。此外请更详焉。窃尝并孟子与告子论性四章而合观之。告子杞柳湍水食色之说。或以为恶。或以为无分于善恶者。盖皆由于认气质为性。故其说虽多端。要皆不出于生之谓性一言之意也。是以孟子辟其说。每以性善为言。而其剖析性气。(不析性气。无以见性之善。)直指本善。而义精辞切者。又莫如此章之所辨也。今谓此章告子之说。不惟无改于前后。又其为根本者。而孟子所辨。却舍其前后所主性善之指。遽变为他说者。其果成说乎。此一误也。且既以此章孟子所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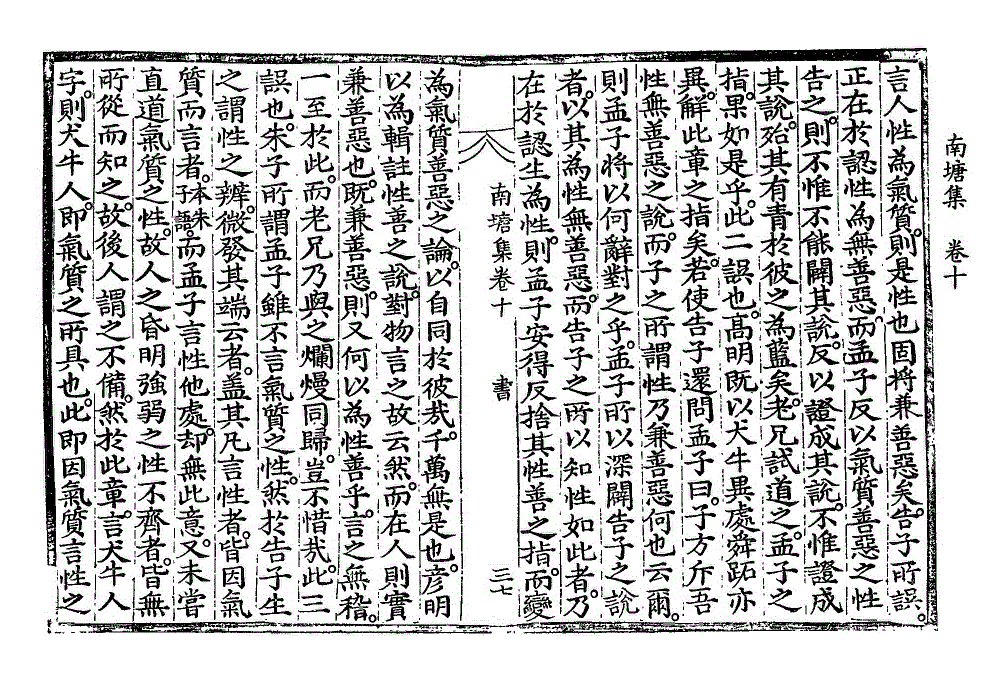 言人性为气质。则是性也固将兼善恶矣。告子所误。正在于认性为无善恶。而孟子反以气质善恶之性告之。则不惟不能辟其说。反以證成其说。不惟證成其说。殆其有青于彼之为蓝矣。老兄试道之。孟子之指。果如是乎。此二误也。高明既以犬牛异处舜蹠亦异。解此章之指矣。若使告子还问孟子曰。子方斥吾性无善恶之说。而子之所谓性乃兼善恶何也云尔。则孟子将以何辞对之乎。孟子所以深辟告子之说者。以其为性无善恶。而告子之所以知性如此者。乃在于认生为性。则孟子安得反舍其性善之指。而变为气质善恶之论。以自同于彼哉。千万无是也。彦明以为辑注性善之说。对物言之故云然。而在人则实兼善恶也。既兼善恶。则又何以为性善乎。言之无稽。一至于此。而老兄乃与之烂熳同归。岂不惜哉。此三误也。朱子所谓孟子虽不言气质之性。然于告子生之谓性之辨。微发其端云者。盖其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者。(本朱子语。)而孟子言性他处。却无此意。又未尝直道气质之性。故人之昏明强弱之性不齐者。皆无所从而知之。故后人谓之不备。然于此章。言犬牛人字。则犬牛人。即气质之所具也。此即因气质言性之
言人性为气质。则是性也固将兼善恶矣。告子所误。正在于认性为无善恶。而孟子反以气质善恶之性告之。则不惟不能辟其说。反以證成其说。不惟證成其说。殆其有青于彼之为蓝矣。老兄试道之。孟子之指。果如是乎。此二误也。高明既以犬牛异处舜蹠亦异。解此章之指矣。若使告子还问孟子曰。子方斥吾性无善恶之说。而子之所谓性乃兼善恶何也云尔。则孟子将以何辞对之乎。孟子所以深辟告子之说者。以其为性无善恶。而告子之所以知性如此者。乃在于认生为性。则孟子安得反舍其性善之指。而变为气质善恶之论。以自同于彼哉。千万无是也。彦明以为辑注性善之说。对物言之故云然。而在人则实兼善恶也。既兼善恶。则又何以为性善乎。言之无稽。一至于此。而老兄乃与之烂熳同归。岂不惜哉。此三误也。朱子所谓孟子虽不言气质之性。然于告子生之谓性之辨。微发其端云者。盖其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者。(本朱子语。)而孟子言性他处。却无此意。又未尝直道气质之性。故人之昏明强弱之性不齐者。皆无所从而知之。故后人谓之不备。然于此章。言犬牛人字。则犬牛人。即气质之所具也。此即因气质言性之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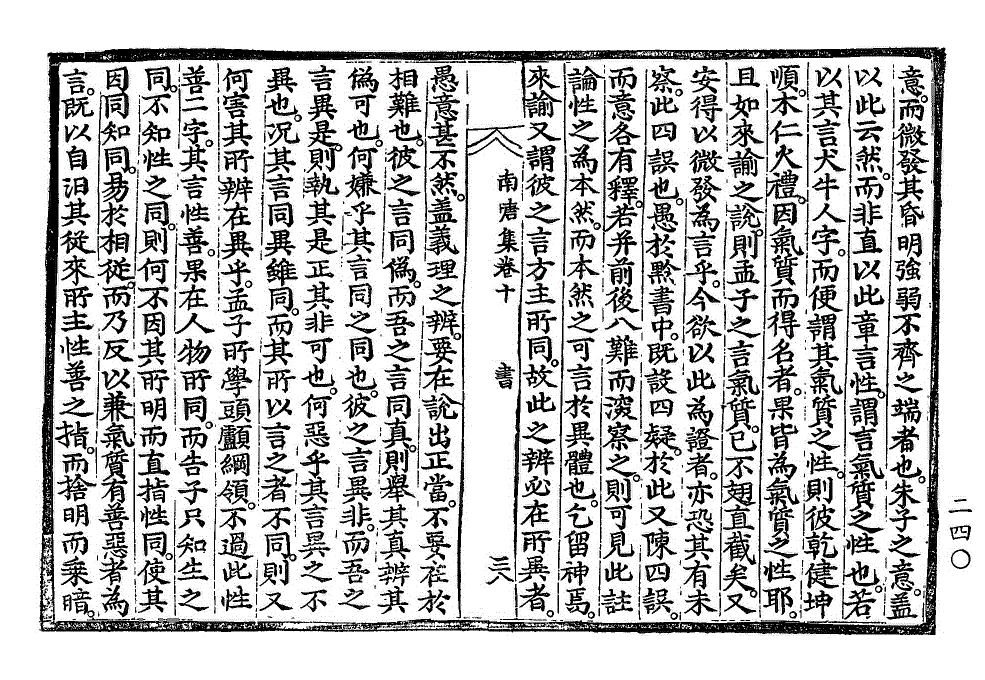 意。而微发其昏明强弱不齐之端者也。朱子之意。盖以此云然。而非直以此章言性。谓言气质之性也。若以其言犬牛人字。而便谓其气质之性。则彼乾健坤顺。木仁火礼。因气质而得名者。果皆为气质之性耶。且如来谕之说。则孟子之言气质。已不翅直截矣。又安得以微发为言乎。今欲以此为證者。亦恐其有未察。此四误也。愚于黔书中。既设四疑。于此又陈四误。而意各有释。若并前后八难而深察之。则可见此注论性之为本然。而本然之可言于异体也。乞留神焉。来谕又谓彼之言方主所同。故此之辨必在所异者。愚意甚不然。盖义理之辨。要在说出正当。不要在于相难也。彼之言同伪。而吾之言同真。则举其真辨其伪可也。何嫌乎其言同之同也。彼之言异非。而吾之言异是。则执其是正其非可也。何恶乎其言异之不异也。况其言同异虽同。而其所以言之者不同。则又何害其所辨在异乎。孟子所学头颅纲领。不过此性善二字。其言性善。果在人物所同。而告子只知生之同。不知性之同。则何不因其所明而直指性同。使其因同知同。易于相从。而乃反以兼气质有善恶者为言。既以自汨其从来所主性善之指。而舍明而乘暗。
意。而微发其昏明强弱不齐之端者也。朱子之意。盖以此云然。而非直以此章言性。谓言气质之性也。若以其言犬牛人字。而便谓其气质之性。则彼乾健坤顺。木仁火礼。因气质而得名者。果皆为气质之性耶。且如来谕之说。则孟子之言气质。已不翅直截矣。又安得以微发为言乎。今欲以此为證者。亦恐其有未察。此四误也。愚于黔书中。既设四疑。于此又陈四误。而意各有释。若并前后八难而深察之。则可见此注论性之为本然。而本然之可言于异体也。乞留神焉。来谕又谓彼之言方主所同。故此之辨必在所异者。愚意甚不然。盖义理之辨。要在说出正当。不要在于相难也。彼之言同伪。而吾之言同真。则举其真辨其伪可也。何嫌乎其言同之同也。彼之言异非。而吾之言异是。则执其是正其非可也。何恶乎其言异之不异也。况其言同异虽同。而其所以言之者不同。则又何害其所辨在异乎。孟子所学头颅纲领。不过此性善二字。其言性善。果在人物所同。而告子只知生之同。不知性之同。则何不因其所明而直指性同。使其因同知同。易于相从。而乃反以兼气质有善恶者为言。既以自汨其从来所主性善之指。而舍明而乘暗。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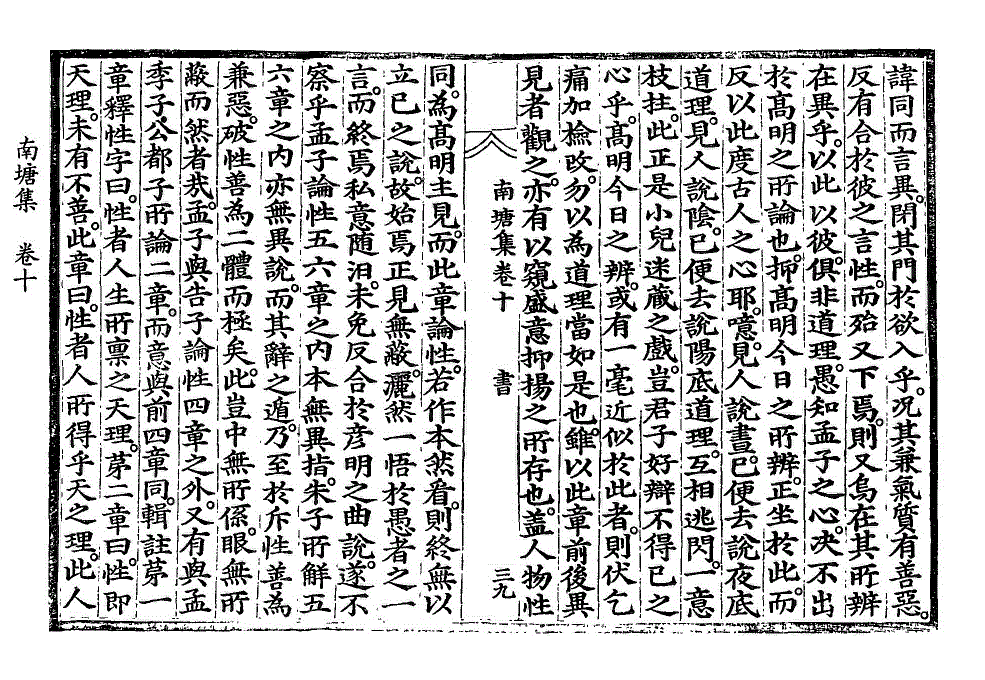 讳同而言异。闭其门于欲入乎。况其兼气质有善恶。反有合于彼之言性。而殆又下焉。则又乌在其所辨在异乎。以此以彼。俱非道理。愚知孟子之心。决不出于高明之所论也。抑高明今日之所辨。正坐于此。而反以此度古人之心耶。噫。见人说昼。己便去说夜底道理。见人说阴。己便去说阳底道理。互相逃闪。一意枝拄。此正是小儿迷藏之戏。岂君子好辩不得已之心乎。高明今日之辨。或有一毫近似于此者。则伏乞痛加检改。勿以为道理当如是也。虽以此章前后异见者观之。亦有以窥盛意抑扬之所存也。盖人物性同。为高明主见。而此章论性。若作本然看。则终无以立己之说。故始焉正见无蔽。洒然一悟于愚者之一言。而终焉私意随汨。未免反合于彦明之曲说。遂不察乎孟子论性五六章之内本无异指。朱子所解五六章之内亦无异说。而其辞之遁。乃至于斥性善为兼恶。破性善为二体而极矣。此岂中无所系。眼无所蔽而然者哉。孟子与告子论性四章之外。又有与孟季子,公都子所论二章。而意与前四章同。辑注第一章释性字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第二章曰。性即天理。未有不善。此章曰。性者人所得乎天之理。此人
讳同而言异。闭其门于欲入乎。况其兼气质有善恶。反有合于彼之言性。而殆又下焉。则又乌在其所辨在异乎。以此以彼。俱非道理。愚知孟子之心。决不出于高明之所论也。抑高明今日之所辨。正坐于此。而反以此度古人之心耶。噫。见人说昼。己便去说夜底道理。见人说阴。己便去说阳底道理。互相逃闪。一意枝拄。此正是小儿迷藏之戏。岂君子好辩不得已之心乎。高明今日之辨。或有一毫近似于此者。则伏乞痛加检改。勿以为道理当如是也。虽以此章前后异见者观之。亦有以窥盛意抑扬之所存也。盖人物性同。为高明主见。而此章论性。若作本然看。则终无以立己之说。故始焉正见无蔽。洒然一悟于愚者之一言。而终焉私意随汨。未免反合于彦明之曲说。遂不察乎孟子论性五六章之内本无异指。朱子所解五六章之内亦无异说。而其辞之遁。乃至于斥性善为兼恶。破性善为二体而极矣。此岂中无所系。眼无所蔽而然者哉。孟子与告子论性四章之外。又有与孟季子,公都子所论二章。而意与前四章同。辑注第一章释性字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第二章曰。性即天理。未有不善。此章曰。性者人所得乎天之理。此人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1L 页
 性之所以无不善。第四第五章。引范氏说通论曰。明仁义之在内。则知人之性善。第六章。引程子说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前后所释。无一言不同。今曰前后五章之注皆言性善。而此章之注独言气质者。其果成说乎。又况此章。乃朱子所谓告子迷谬之根本。孟子开示之要切者。而辑注之训释特详焉。则他章之说。亦当自此推知。况可以此为六章之别义乎。且孟子之道性善。始见于滕文公首章。而辑注曰。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其说果与此章所释。亦有一字不同者耶。孟子此章言性。果为气质。则其所道于滕文公者。亦当准此。而七篇之中。将无一字言性之善矣。高论又谓告子认气为性。而孟子以理言性。此其所以不同而辟彼之说也。此尤不然。前人之以理言性者。皆指本然。而今以为气质。则其谬甚矣。况告子方以气之无分于善恶者为性。而孟子乃以理之一定于善恶者为性。则愚恐孟子之走。已先占过告子之百步矣。其何说之可辟乎。他人误见。尚可异也。况于老兄乎。愿更详之。
性之所以无不善。第四第五章。引范氏说通论曰。明仁义之在内。则知人之性善。第六章。引程子说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前后所释。无一言不同。今曰前后五章之注皆言性善。而此章之注独言气质者。其果成说乎。又况此章。乃朱子所谓告子迷谬之根本。孟子开示之要切者。而辑注之训释特详焉。则他章之说。亦当自此推知。况可以此为六章之别义乎。且孟子之道性善。始见于滕文公首章。而辑注曰。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其说果与此章所释。亦有一字不同者耶。孟子此章言性。果为气质。则其所道于滕文公者。亦当准此。而七篇之中。将无一字言性之善矣。高论又谓告子认气为性。而孟子以理言性。此其所以不同而辟彼之说也。此尤不然。前人之以理言性者。皆指本然。而今以为气质。则其谬甚矣。况告子方以气之无分于善恶者为性。而孟子乃以理之一定于善恶者为性。则愚恐孟子之走。已先占过告子之百步矣。其何说之可辟乎。他人误见。尚可异也。况于老兄乎。愿更详之。函丈尝教云。学者一言一议之失。固无大害。但因此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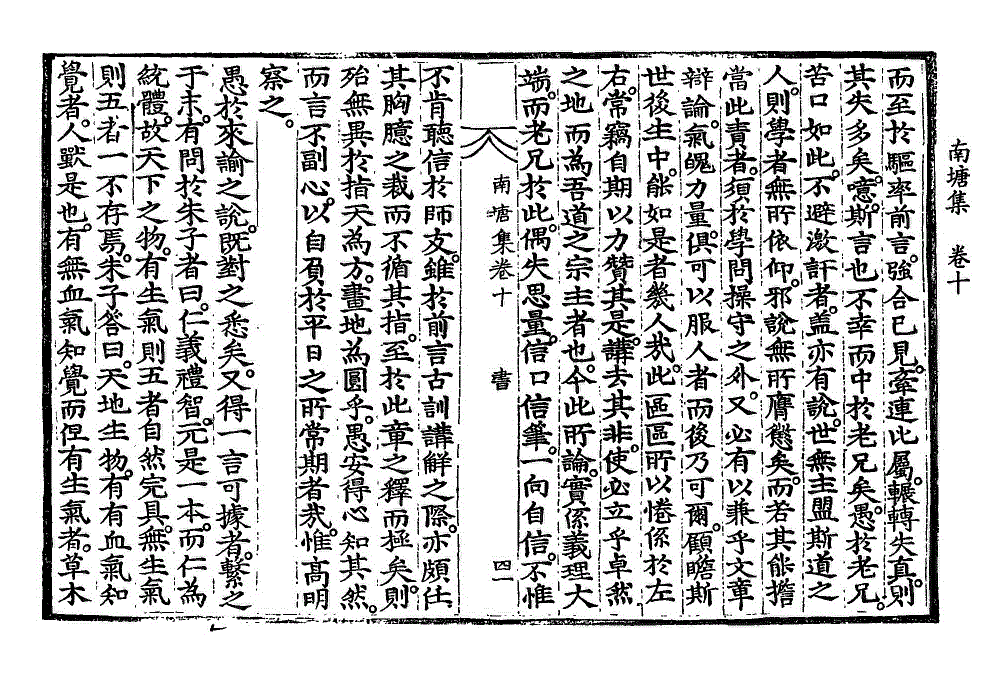 而至于驱率前言。强合己见。牵连比属。辗转失真。则其失多矣。噫。斯言也不幸而中于老兄矣。愚于老兄。苦口如此。不避激讦者。盖亦有说。世无主盟斯道之人。则学者无所依仰。邪说无所膺惩矣。而若其能担当此责者。须于学问操守之外。又必有以兼乎文章辩论。气魄力量。俱可以服人者而后乃可尔。顾瞻斯世后生中。能如是者几人哉。此区区所以惓系于左右。常窃自期以力赞其是。讲去其非。使必立乎卓然之地而为吾道之宗主者也。今此所论。实系义理大端。而老兄于此。偶失思量。信口信笔。一向自信。不惟不肯听信于师友。虽于前言古训讲解之际。亦颇任其胸臆之裁而不循其指。至于此章之释而极矣。则殆无异于指天为方。画地为圆乎。愚安得心知其然。而言不副心。以自负于平日之所常期者哉。惟高明察之。
而至于驱率前言。强合己见。牵连比属。辗转失真。则其失多矣。噫。斯言也不幸而中于老兄矣。愚于老兄。苦口如此。不避激讦者。盖亦有说。世无主盟斯道之人。则学者无所依仰。邪说无所膺惩矣。而若其能担当此责者。须于学问操守之外。又必有以兼乎文章辩论。气魄力量。俱可以服人者而后乃可尔。顾瞻斯世后生中。能如是者几人哉。此区区所以惓系于左右。常窃自期以力赞其是。讲去其非。使必立乎卓然之地而为吾道之宗主者也。今此所论。实系义理大端。而老兄于此。偶失思量。信口信笔。一向自信。不惟不肯听信于师友。虽于前言古训讲解之际。亦颇任其胸臆之裁而不循其指。至于此章之释而极矣。则殆无异于指天为方。画地为圆乎。愚安得心知其然。而言不副心。以自负于平日之所常期者哉。惟高明察之。愚于来谕之说。既对之悉矣。又得一言可据者。系之于末。有问于朱子者曰。仁义礼智。元是一本。而仁为统体。故天下之物。有生气则五者自然完具。无生气则五者一不存焉。朱子答曰。天地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2L 页
 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其理则未尝不同。(所谓理同则可。)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所谓性同则不可。)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但其所以为是物之理。则未尝不具耳。窃观其问者之意。正如老兄之见。而朱子之所答如此。则此问答。岂非为今日准备公案耶。抑老兄又以为此所言五常者。亦其气质而非本然者耶。若然则合下问者直论此性。而未尝问气质。朱子反以气质善恶之性告之。而不告性之本然者何也。以此推之他说。则凡老兄所谓气质之五常者。又安知其皆然耶。老兄曾未见此问答。则从今可释前惑。若已见此而犹自壁立。则窃恐是不择之固执。无益之好胜也。退翁所谓虽使当时举天下之人。无能与我抗其是非者。千万世之下。安知不有圣贤者出。指出我瑕隙。觑破我隐病者。可不惧哉。愿高明善思而更教之。
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其理则未尝不同。(所谓理同则可。)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所谓性同则不可。)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但其所以为是物之理。则未尝不具耳。窃观其问者之意。正如老兄之见。而朱子之所答如此。则此问答。岂非为今日准备公案耶。抑老兄又以为此所言五常者。亦其气质而非本然者耶。若然则合下问者直论此性。而未尝问气质。朱子反以气质善恶之性告之。而不告性之本然者何也。以此推之他说。则凡老兄所谓气质之五常者。又安知其皆然耶。老兄曾未见此问答。则从今可释前惑。若已见此而犹自壁立。则窃恐是不择之固执。无益之好胜也。退翁所谓虽使当时举天下之人。无能与我抗其是非者。千万世之下。安知不有圣贤者出。指出我瑕隙。觑破我隐病者。可不惧哉。愿高明善思而更教之。附二诗奉次求教(二诗首尾。皆用盛句。)
寂然心体湛然明。赋质还他有浊清。理杂气时容有恶。机乘动处便云情。须从这里单言性。方信几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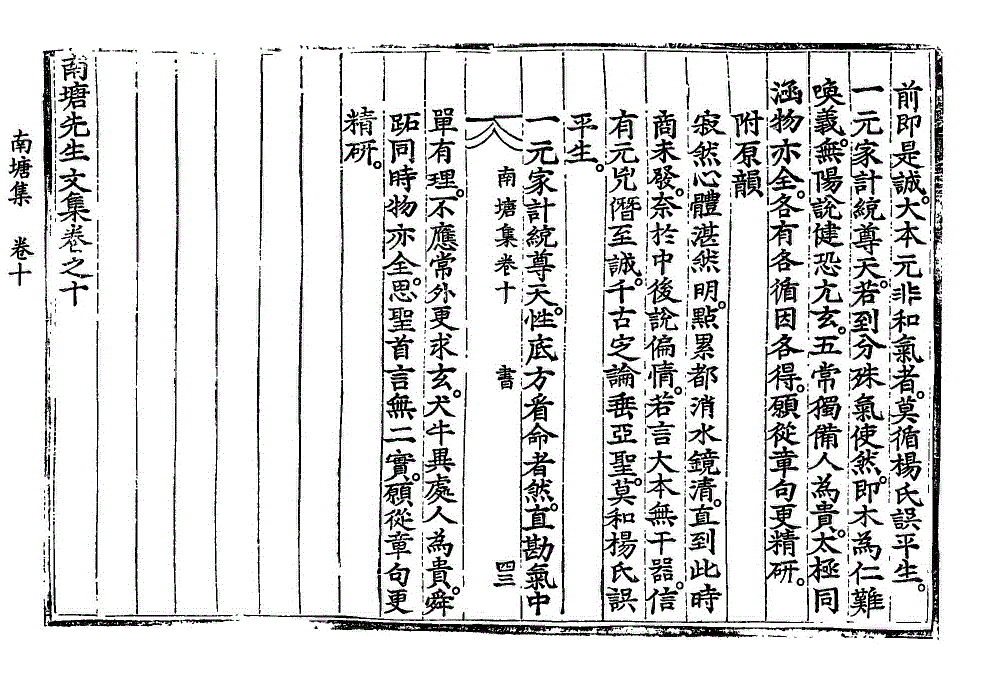 前即是诚。大本元非和气者。莫循杨氏误平生。
前即是诚。大本元非和气者。莫循杨氏误平生。一元家计统尊天。若到分殊气使然。即木为仁难唤义。无阳说健恐尤玄。五常独备人为贵。太极同涵物亦全。各有各循因各得。愿从章句更精研。
附原韵
寂然心体湛然明。点累都消水镜清。直到此时商未发。奈于中后说偏情。若言大本无干器。信有元凶僭至诚。千古定论垂亚圣。莫和杨氏误平生。
一元家计统尊天。性底方看命者然。直勘气中单有理。不应常外更求玄。犬牛异处人为贵。舜蹠同时物亦全。思圣首言无二实。愿从章句更精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