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筵说
筵说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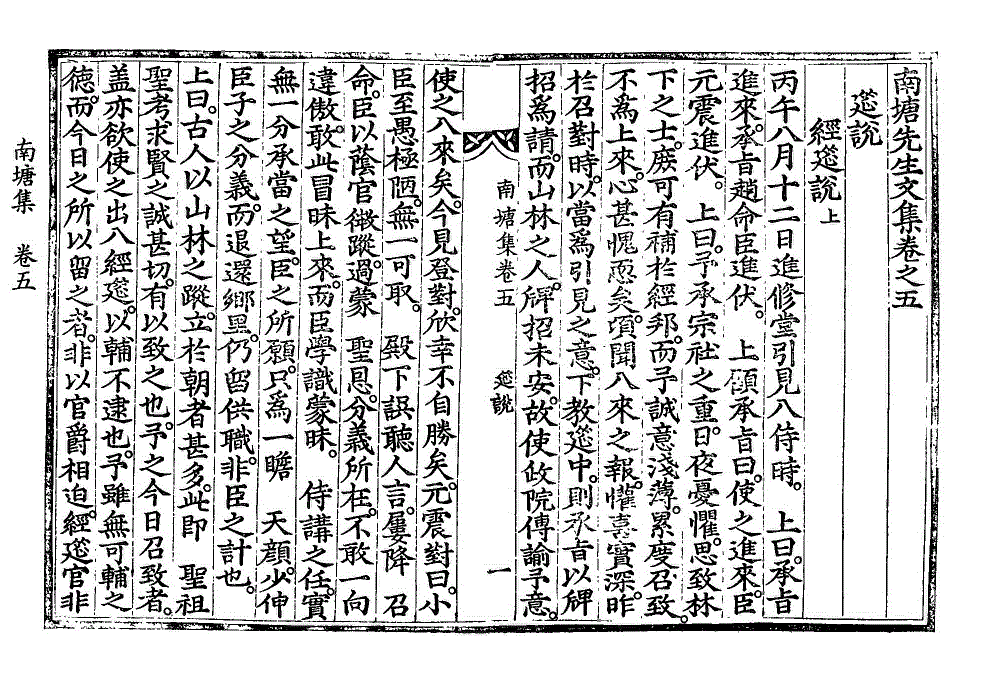 经筵说[上]
经筵说[上]丙午八月十二日进修堂引见入侍时。 上曰。承旨进来。承旨赵命臣进伏。 上顾承旨曰。使之进来。臣元震进伏。 上曰。予承宗社之重。日夜忧惧。思致林下之士。庶可有补于经邦。而予诚意浅薄。累度召致。不为上来。心甚愧恧矣。顷闻入来之报。欢喜实深。昨于召对时。以当为引见之意。下教筵中。则承旨以牌招为请。而山林之人。牌招未安。故使政院传谕予意。使之入来矣。今见登对。欣幸不自胜矣。元震对曰。小臣至愚极陋。无一可取。 殿下误听人言。屡降 召命。臣以荫官微踪。过蒙 圣恩。分义所在。不敢一向违傲。敢此冒昧上来。而臣学识蒙昧。 侍讲之任。实无一分承当之望。臣之所愿。只为一瞻 天颜。少伸臣子之分义。而退还乡里。仍留供职。非臣之计也。 上曰。古人以山林之踪。立于朝者甚多。此即 圣祖圣考求贤之诚甚切。有以致之也。予之今日召致者。盖亦欲使之出入经筵。以辅不逮也。予虽无可辅之德。而今日之所以留之者。非以官爵相迫。经筵官非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9L 页
 实职。留在京中。辅导不逮。是所望也。元震对曰。人主使臣。人臣自处。皆当各适其分。贤者处之以贤。愚者处之以愚。贤愚各得其分。然后上无妄施之讥。下免负乘之患。治道亦可因此而兴。今 殿下所以处臣者则不然。既召臣以不敢当之职任。又下以不敢当之 圣教。臣何敢不自揣分而冒没承当乎。臣以世禄之裔。本非林下之士。故于顷年陵官翊卫司。无不膺 命。臣之本情。于此可见矣。 殿下今若处臣以可堪之道。臣何敢辄为辞避之计哉。 上曰。平日出入于先正之门。必多所学。平时所蕴。须为毕陈。无孤今日赐对之意可也。元震对曰。臣本无学识。岂有所可陈 达者哉。 上曰。勿为过让陈达可也。元震对曰。臣出入先正之门。岁月颇久。所闻于师友者则略有之矣。请以是陈之。臣闻帝王为治。必本于道。所谓道者。非是异常别件物事也。只是天命人心本然之理。日用事物当然之则。其源出于天。而其体具于心。其用著于事。存其心以养其性约其情。则道可得于己矣。人皆有是心是性。道本在我。而能有是道者寡焉何哉。只以人欲间之故也。天理人欲。迭为胜负。一分人欲长。则一分天理消。十分人欲长。则十分天理
实职。留在京中。辅导不逮。是所望也。元震对曰。人主使臣。人臣自处。皆当各适其分。贤者处之以贤。愚者处之以愚。贤愚各得其分。然后上无妄施之讥。下免负乘之患。治道亦可因此而兴。今 殿下所以处臣者则不然。既召臣以不敢当之职任。又下以不敢当之 圣教。臣何敢不自揣分而冒没承当乎。臣以世禄之裔。本非林下之士。故于顷年陵官翊卫司。无不膺 命。臣之本情。于此可见矣。 殿下今若处臣以可堪之道。臣何敢辄为辞避之计哉。 上曰。平日出入于先正之门。必多所学。平时所蕴。须为毕陈。无孤今日赐对之意可也。元震对曰。臣本无学识。岂有所可陈 达者哉。 上曰。勿为过让陈达可也。元震对曰。臣出入先正之门。岁月颇久。所闻于师友者则略有之矣。请以是陈之。臣闻帝王为治。必本于道。所谓道者。非是异常别件物事也。只是天命人心本然之理。日用事物当然之则。其源出于天。而其体具于心。其用著于事。存其心以养其性约其情。则道可得于己矣。人皆有是心是性。道本在我。而能有是道者寡焉何哉。只以人欲间之故也。天理人欲。迭为胜负。一分人欲长。则一分天理消。十分人欲长。则十分天理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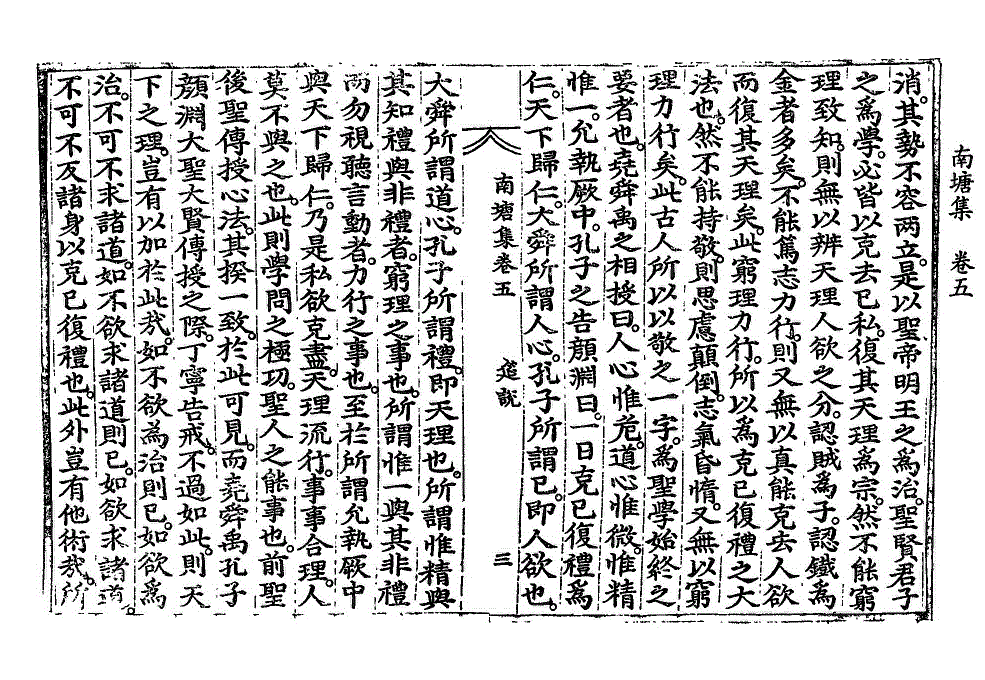 消。其势不容两立。是以圣帝明王之为治。圣贤君子之为学。必皆以克去己私。复其天理为宗。然不能穷理致知。则无以辨天理人欲之分。认贼为子。认铁为金者多矣。不能笃志力行。则又无以真能克去人欲而复其天理矣。此穷理力行。所以为克己复礼之大法也。然不能持敬。则思虑颠倒。志气昏惰。又无以穷理力行矣。此古人所以以敬之一字。为圣学始终之要者也。尧舜禹之相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之告颜渊曰。一日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大舜所谓人心。孔子所谓己。即人欲也。大舜所谓道心。孔子所谓礼。即天理也。所谓惟精与其知礼与非礼者。穷理之事也。所谓惟一与其非礼而勿视听言动者。力行之事也。至于所谓允执厥中与天下归仁。乃是私欲克尽。天理流行。事事合理。人莫不与之也。此则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也。前圣后圣传授心法。其揆一致。于此可见。而尧舜禹孔子颜渊大圣大贤传授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如不欲为治则已。如欲为治。不可不求诸道。如不欲求诸道则已。如欲求诸道。不可不反诸身以克己复礼也。此外岂有他术哉。所
消。其势不容两立。是以圣帝明王之为治。圣贤君子之为学。必皆以克去己私。复其天理为宗。然不能穷理致知。则无以辨天理人欲之分。认贼为子。认铁为金者多矣。不能笃志力行。则又无以真能克去人欲而复其天理矣。此穷理力行。所以为克己复礼之大法也。然不能持敬。则思虑颠倒。志气昏惰。又无以穷理力行矣。此古人所以以敬之一字。为圣学始终之要者也。尧舜禹之相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之告颜渊曰。一日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大舜所谓人心。孔子所谓己。即人欲也。大舜所谓道心。孔子所谓礼。即天理也。所谓惟精与其知礼与非礼者。穷理之事也。所谓惟一与其非礼而勿视听言动者。力行之事也。至于所谓允执厥中与天下归仁。乃是私欲克尽。天理流行。事事合理。人莫不与之也。此则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也。前圣后圣传授心法。其揆一致。于此可见。而尧舜禹孔子颜渊大圣大贤传授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如不欲为治则已。如欲为治。不可不求诸道。如不欲求诸道则已。如欲求诸道。不可不反诸身以克己复礼也。此外岂有他术哉。所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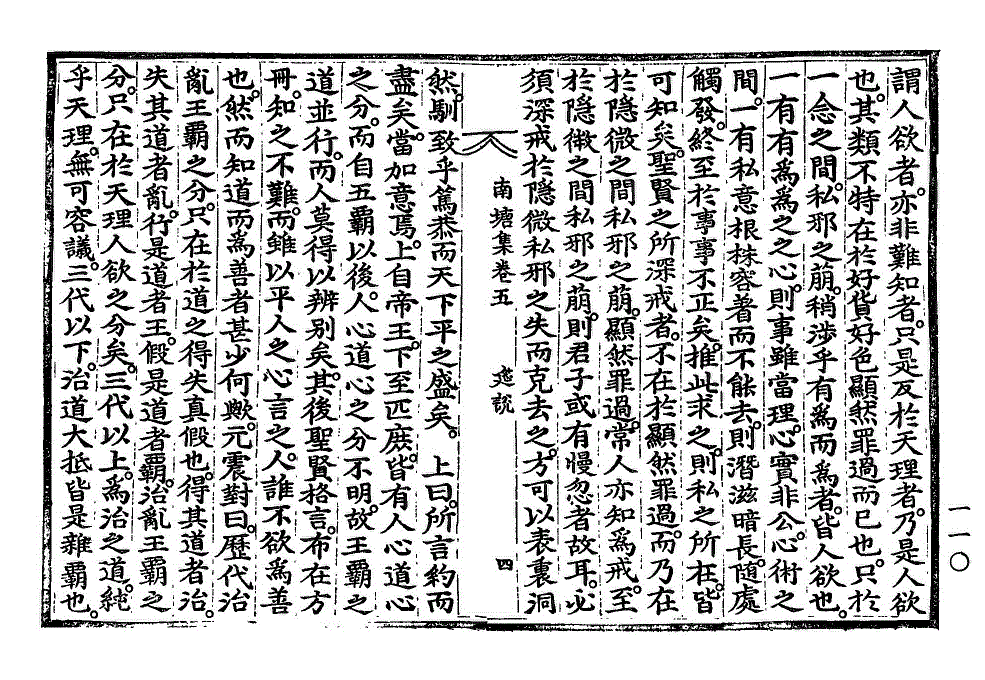 谓人欲者。亦非难知者。只是反于天理者。乃是人欲也。其类不特在于好货好色显然罪过而已也。只于一念之间。私邪之萌。稍涉乎有为而为者。皆人欲也。一有有为为之之心。则事虽当理。心实非公。心术之间。一有私意根株容着而不能去。则潜滋暗长。随处触发。终至于事事不正矣。推此求之。则私之所在。皆可知矣。圣贤之所深戒者。不在于显然罪过。而乃在于隐微之间私邪之萌。显然罪过。常人亦知为戒。至于隐微之间私邪之萌。则君子或有慢忽者故耳。必须深戒于隐微私邪之失而克去之。方可以表里洞然。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矣。 上曰。所言约而尽矣。当加意焉。上自帝王。下至匹庶。皆有人心道心之分。而自五霸以后。人心道心之分不明。故王霸之道并行。而人莫得以辨别矣。其后圣贤格言。布在方册。知之不难。而虽以平人之心言之。人谁不欲为善也。然而知道而为善者甚少何欤。元震对曰。历代治乱王霸之分。只在于道之得失真假也。得其道者治。失其道者乱。行是道者王。假是道者霸。治乱王霸之分。只在于天理人欲之分矣。三代以上。为治之道。纯乎天理。无可容议。三代以下。治道大抵皆是杂霸也。
谓人欲者。亦非难知者。只是反于天理者。乃是人欲也。其类不特在于好货好色显然罪过而已也。只于一念之间。私邪之萌。稍涉乎有为而为者。皆人欲也。一有有为为之之心。则事虽当理。心实非公。心术之间。一有私意根株容着而不能去。则潜滋暗长。随处触发。终至于事事不正矣。推此求之。则私之所在。皆可知矣。圣贤之所深戒者。不在于显然罪过。而乃在于隐微之间私邪之萌。显然罪过。常人亦知为戒。至于隐微之间私邪之萌。则君子或有慢忽者故耳。必须深戒于隐微私邪之失而克去之。方可以表里洞然。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矣。 上曰。所言约而尽矣。当加意焉。上自帝王。下至匹庶。皆有人心道心之分。而自五霸以后。人心道心之分不明。故王霸之道并行。而人莫得以辨别矣。其后圣贤格言。布在方册。知之不难。而虽以平人之心言之。人谁不欲为善也。然而知道而为善者甚少何欤。元震对曰。历代治乱王霸之分。只在于道之得失真假也。得其道者治。失其道者乱。行是道者王。假是道者霸。治乱王霸之分。只在于天理人欲之分矣。三代以上。为治之道。纯乎天理。无可容议。三代以下。治道大抵皆是杂霸也。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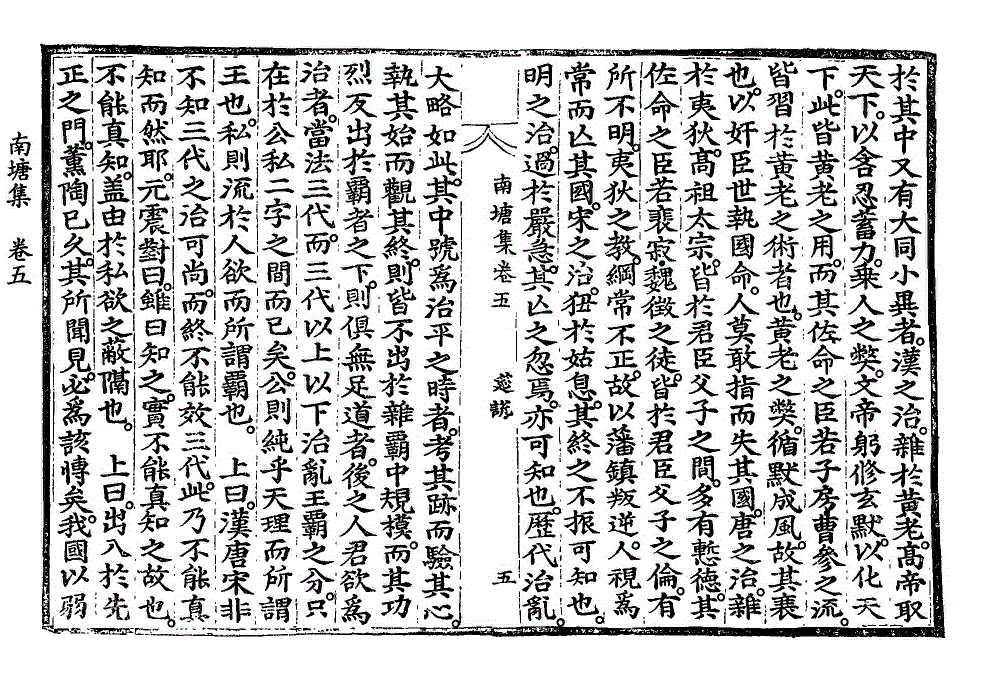 于其中又有大同小异者。汉之治。杂于黄老。高帝取天下。以含忍蓄力。乘人之弊。文帝躬修玄默。以化天下。此皆黄老之用。而其佐命之臣若子房,曹参之流。皆习于黄老之术者也。黄老之弊。循默成风。故其衰也。以奸臣世执国命。人莫敢指而失其国。唐之治。杂于夷狄。高祖太宗。皆于君臣父子之间。多有惭德。其佐命之臣若裴寂,魏徵之徒。皆于君臣父子之伦。有所不明。夷狄之教。纲常不正。故以藩镇叛逆。人视为常而亡其国。宋之治。狃于姑息。其终之不振可知也。明之治。过于严急。其亡之忽焉。亦可知也。历代治乱。大略如此。其中号为治平之时者。考其迹而验其心。执其始而观其终。则皆不出于杂霸中规模。而其功烈反出于霸者之下。则俱无足道者。后之人君欲为治者。当法三代。而三代以上以下治乱王霸之分。只在于公私二字之间而已矣。公则纯乎天理而所谓王也。私则流于人欲而所谓霸也。 上曰。汉唐宋非不知三代之治可尚。而终不能效三代。此乃不能真知而然耶。元震对曰。虽曰知之。实不能真知之故也。不能真知。盖由于私欲之蔽隔也。 上曰。出入于先正之门。薰陶已久。其所闻见。必为该博矣。我国以弱
于其中又有大同小异者。汉之治。杂于黄老。高帝取天下。以含忍蓄力。乘人之弊。文帝躬修玄默。以化天下。此皆黄老之用。而其佐命之臣若子房,曹参之流。皆习于黄老之术者也。黄老之弊。循默成风。故其衰也。以奸臣世执国命。人莫敢指而失其国。唐之治。杂于夷狄。高祖太宗。皆于君臣父子之间。多有惭德。其佐命之臣若裴寂,魏徵之徒。皆于君臣父子之伦。有所不明。夷狄之教。纲常不正。故以藩镇叛逆。人视为常而亡其国。宋之治。狃于姑息。其终之不振可知也。明之治。过于严急。其亡之忽焉。亦可知也。历代治乱。大略如此。其中号为治平之时者。考其迹而验其心。执其始而观其终。则皆不出于杂霸中规模。而其功烈反出于霸者之下。则俱无足道者。后之人君欲为治者。当法三代。而三代以上以下治乱王霸之分。只在于公私二字之间而已矣。公则纯乎天理而所谓王也。私则流于人欲而所谓霸也。 上曰。汉唐宋非不知三代之治可尚。而终不能效三代。此乃不能真知而然耶。元震对曰。虽曰知之。实不能真知之故也。不能真知。盖由于私欲之蔽隔也。 上曰。出入于先正之门。薰陶已久。其所闻见。必为该博矣。我国以弱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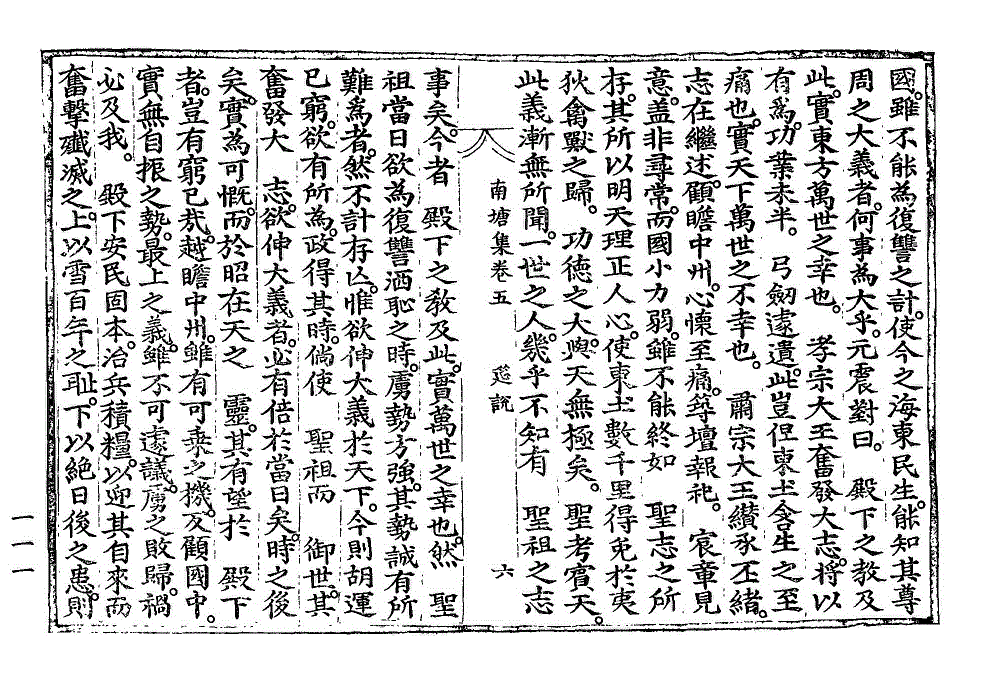 国。虽不能为复雠之计。使今之海东民生。能知其尊周之大义者。何事为大乎。元震对曰。 殿下之教及此。实东方万世之幸也。 孝宗大王奋发大志。将以有为。功业未半。 弓剑遽遗。此岂但东土含生之至痛也。实天下万世之不幸也。 肃宗大王缵承丕绪。志在继述。顾瞻中州。心怀至痛。筑坛报祀。 宸章见意。盖非寻常。而国小力弱。虽不能终如 圣志之所存。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使东土数千里得免于夷狄禽兽之归。 功德之大。与天无极矣。 圣考宾天。此义渐无所闻。一世之人。几乎不知有 圣祖之志事矣。今者 殿下之教及此。实万世之幸也。然 圣祖当日欲为复雠洒耻之时。虏势方强。其势诚有所难为者。然不计存亡。惟欲伸大义于天下。今则胡运已穷。欲有所为。政得其时。倘使 圣祖而 御世。其奋发大 志。欲伸大义者。必有倍于当日矣。时之后矣。实为可慨。而于昭在天之 灵。其有望于 殿下者。岂有穷已哉。越瞻中州。虽有可乘之机。反顾国中。实无自振之势。最上之义。虽不可遽议。虏之败归。祸必及我。 殿下安民固本。治兵积粮。以迎其自来而奋击歼灭之。上以雪百年之耻。下以绝日后之患。则
国。虽不能为复雠之计。使今之海东民生。能知其尊周之大义者。何事为大乎。元震对曰。 殿下之教及此。实东方万世之幸也。 孝宗大王奋发大志。将以有为。功业未半。 弓剑遽遗。此岂但东土含生之至痛也。实天下万世之不幸也。 肃宗大王缵承丕绪。志在继述。顾瞻中州。心怀至痛。筑坛报祀。 宸章见意。盖非寻常。而国小力弱。虽不能终如 圣志之所存。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使东土数千里得免于夷狄禽兽之归。 功德之大。与天无极矣。 圣考宾天。此义渐无所闻。一世之人。几乎不知有 圣祖之志事矣。今者 殿下之教及此。实万世之幸也。然 圣祖当日欲为复雠洒耻之时。虏势方强。其势诚有所难为者。然不计存亡。惟欲伸大义于天下。今则胡运已穷。欲有所为。政得其时。倘使 圣祖而 御世。其奋发大 志。欲伸大义者。必有倍于当日矣。时之后矣。实为可慨。而于昭在天之 灵。其有望于 殿下者。岂有穷已哉。越瞻中州。虽有可乘之机。反顾国中。实无自振之势。最上之义。虽不可遽议。虏之败归。祸必及我。 殿下安民固本。治兵积粮。以迎其自来而奋击歼灭之。上以雪百年之耻。下以绝日后之患。则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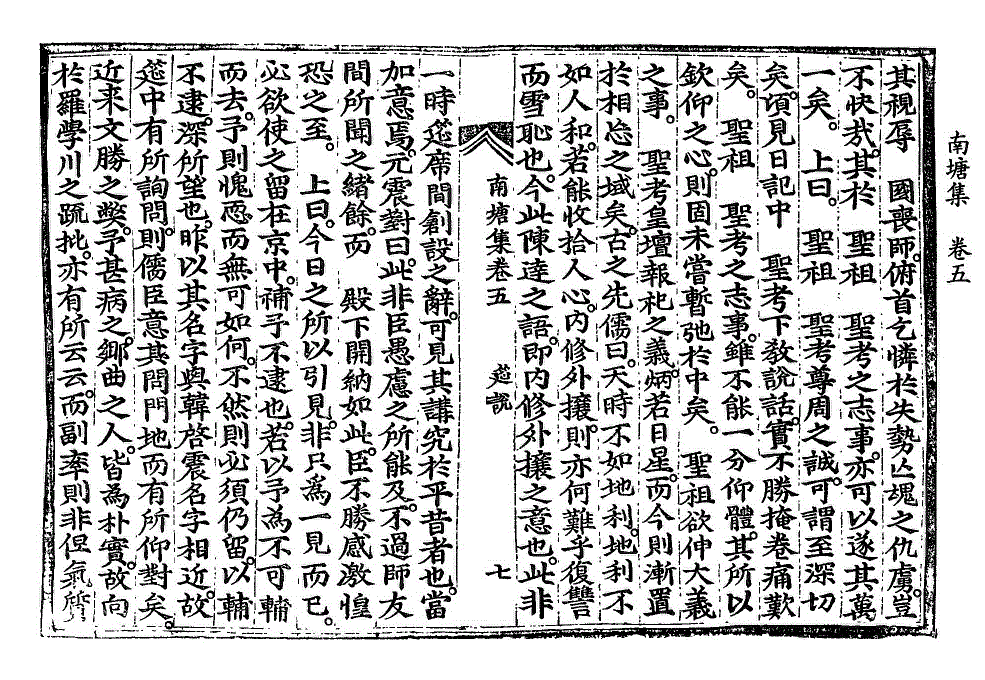 其视辱 国丧师。俯首乞怜于失势亡魂之仇虏。岂不快哉。其于 圣祖 圣考之志事。亦可以遂其万一矣。 上曰。 圣祖 圣考尊周之诚。可谓至深切矣。顷见日记中 圣考下教说话。实不胜掩卷痛叹矣。 圣祖 圣考之志事。虽不能一分仰体。其所以钦仰之心。则固未尝暂弛于中矣。 圣祖欲伸大义之事。 圣考皇坛报祀之义。炳若日星。而今则渐置于相忘之域矣。古之先儒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能收拾人心。内修外攘。则亦何难乎复雠而雪耻也。今此陈达之语。即内修外攘之意也。此非一时筵席间创设之辞。可见其讲究于平昔者也。当加意焉。元震对曰。此非臣愚虑之所能及。不过师友间所闻之绪馀。而 殿下开纳如此。臣不胜感激惶恐之至。 上曰。今日之所以引见。非只为一见而已。必欲使之留在京中。补予不逮也。若以予为不可辅而去。予则愧恧而无可如何。不然则必须仍留。以辅不逮。深所望也。昨以其名字与韩启震名字相近。故筵中有所询问。则儒臣意其问门地而有所仰对矣。近来文胜之弊。予甚病之。乡曲之人。皆为朴实。故向于罗学川之疏批。亦有所云云。而副率则非但气质
其视辱 国丧师。俯首乞怜于失势亡魂之仇虏。岂不快哉。其于 圣祖 圣考之志事。亦可以遂其万一矣。 上曰。 圣祖 圣考尊周之诚。可谓至深切矣。顷见日记中 圣考下教说话。实不胜掩卷痛叹矣。 圣祖 圣考之志事。虽不能一分仰体。其所以钦仰之心。则固未尝暂弛于中矣。 圣祖欲伸大义之事。 圣考皇坛报祀之义。炳若日星。而今则渐置于相忘之域矣。古之先儒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能收拾人心。内修外攘。则亦何难乎复雠而雪耻也。今此陈达之语。即内修外攘之意也。此非一时筵席间创设之辞。可见其讲究于平昔者也。当加意焉。元震对曰。此非臣愚虑之所能及。不过师友间所闻之绪馀。而 殿下开纳如此。臣不胜感激惶恐之至。 上曰。今日之所以引见。非只为一见而已。必欲使之留在京中。补予不逮也。若以予为不可辅而去。予则愧恧而无可如何。不然则必须仍留。以辅不逮。深所望也。昨以其名字与韩启震名字相近。故筵中有所询问。则儒臣意其问门地而有所仰对矣。近来文胜之弊。予甚病之。乡曲之人。皆为朴实。故向于罗学川之疏批。亦有所云云。而副率则非但气质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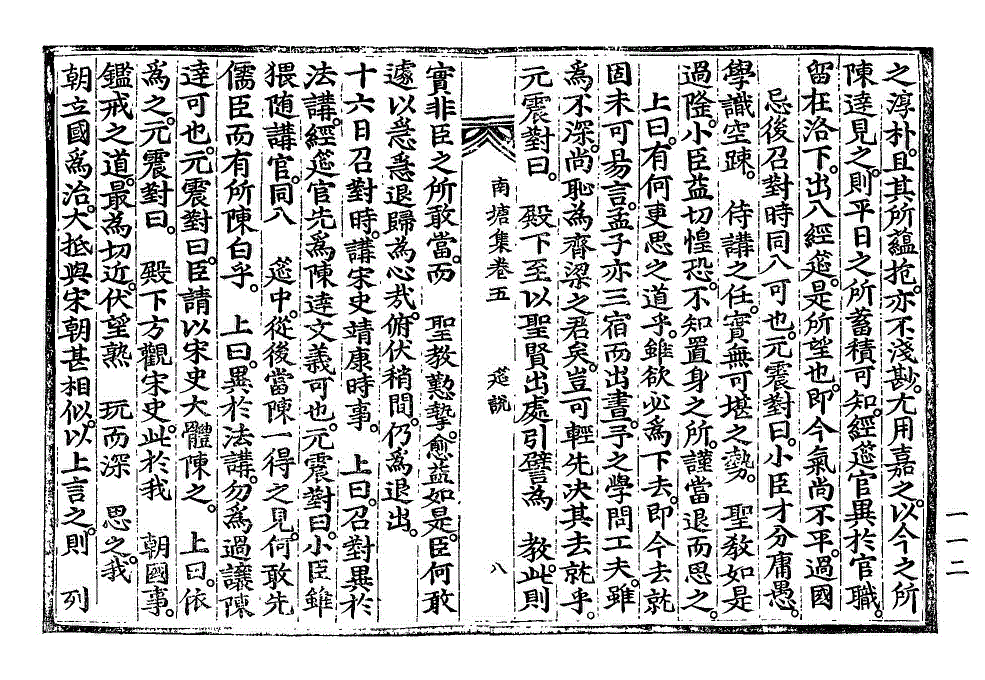 之淳朴。且其所蕴抱。亦不浅鲜。尤用嘉之。以今之所陈达见之。则平日之所蓄积可知。经筵官异于官职。留在洛下。出入经筵。是所望也。即今气尚不平。过国 忌后召对时同入可也。元震对曰。小臣才分庸愚。学识空疏。 侍讲之任。实无可堪之势。 圣教如是过隆。小臣益切惶恐。不知置身之所。谨当退而思之。 上曰。有何更思之道乎。虽欲必为下去。即今去就固未可易言。孟子亦三宿而出昼。予之学问工夫。虽为不深。尚耻为齐梁之君矣。岂可轻先决其去就乎。元震对曰。 殿下至以圣贤出处引譬为 教。此则实非臣之所敢当。而 圣教勤挚。愈益如是。臣何敢遽以急急退归为心哉。俯伏稍间。仍为退出。
之淳朴。且其所蕴抱。亦不浅鲜。尤用嘉之。以今之所陈达见之。则平日之所蓄积可知。经筵官异于官职。留在洛下。出入经筵。是所望也。即今气尚不平。过国 忌后召对时同入可也。元震对曰。小臣才分庸愚。学识空疏。 侍讲之任。实无可堪之势。 圣教如是过隆。小臣益切惶恐。不知置身之所。谨当退而思之。 上曰。有何更思之道乎。虽欲必为下去。即今去就固未可易言。孟子亦三宿而出昼。予之学问工夫。虽为不深。尚耻为齐梁之君矣。岂可轻先决其去就乎。元震对曰。 殿下至以圣贤出处引譬为 教。此则实非臣之所敢当。而 圣教勤挚。愈益如是。臣何敢遽以急急退归为心哉。俯伏稍间。仍为退出。十六日召对时。讲宋史靖康时事。 上曰。召对异于法讲。经筵官先为陈达文义可也。元震对曰。小臣虽猥随讲官。同入 筵中。从后当陈一得之见。何敢先儒臣而有所陈白乎。 上曰。异于法讲。勿为过让陈达可也。元震对曰。臣请以宋史大体陈之。 上曰。依为之。元震对曰。 殿下方观宋史。此于我 朝国事。鉴戒之道。最为切近。伏望熟 玩而深 思之。我 朝立国为治。大抵与宋朝甚相似。以上言之。则 列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3H 页
 圣修身之严。家法之正。崇儒重道。培养士气。同于宋朝。以治道言。则文教太胜。而武略不竞。人才虽多。而办事者少。亦同于宋。宋之武略不竞。故自始每为夷狄所凌逼。卒亡于夷狄。宋之人才。韩琦,范仲淹最为第一。而区区一元昊。韩,范二人身为大帅。亲自当之。终不能制之。不免丧师蹙境之耻。反不如汉唐一偏将提偏师。克敌制胜之为。故朱子尝叹韩,范诸公亦少做事之才。其他又可知矣。我 朝壬辰丙丁之难。皆为贼所败。而至今不免皮币事狄之耻。 国朝以来。名臣硕辅。不为不多。至于当大难。独当一面。能成大功者。亦未之闻。此同于宋朝也。搢绅分党。今过百年。其害日甚。亦如宋之元佑熙礼之党。互相胜负。历累朝而相争者。其他政令之间。规模气像。委靡姑息。亦皆相同。 殿下观宋之事。必反观于我国。其好处之同者。益加勉焉。与同其治。其不好处之同者。深惩而力反之。勿与同其乱。则其于观史鉴戒之道。庶有实得之效矣。臣之所窃忧者。宋朝党祸之馀。遂有靖康之祸。我 朝党祸。亦至于辛壬之年而极矣。深恐此后复有难言之祸。如宋之致败也。此盖腹心内溃。外患必至。譬如木心内伤。风雨蹶拔者矣。总言今日
圣修身之严。家法之正。崇儒重道。培养士气。同于宋朝。以治道言。则文教太胜。而武略不竞。人才虽多。而办事者少。亦同于宋。宋之武略不竞。故自始每为夷狄所凌逼。卒亡于夷狄。宋之人才。韩琦,范仲淹最为第一。而区区一元昊。韩,范二人身为大帅。亲自当之。终不能制之。不免丧师蹙境之耻。反不如汉唐一偏将提偏师。克敌制胜之为。故朱子尝叹韩,范诸公亦少做事之才。其他又可知矣。我 朝壬辰丙丁之难。皆为贼所败。而至今不免皮币事狄之耻。 国朝以来。名臣硕辅。不为不多。至于当大难。独当一面。能成大功者。亦未之闻。此同于宋朝也。搢绅分党。今过百年。其害日甚。亦如宋之元佑熙礼之党。互相胜负。历累朝而相争者。其他政令之间。规模气像。委靡姑息。亦皆相同。 殿下观宋之事。必反观于我国。其好处之同者。益加勉焉。与同其治。其不好处之同者。深惩而力反之。勿与同其乱。则其于观史鉴戒之道。庶有实得之效矣。臣之所窃忧者。宋朝党祸之馀。遂有靖康之祸。我 朝党祸。亦至于辛壬之年而极矣。深恐此后复有难言之祸。如宋之致败也。此盖腹心内溃。外患必至。譬如木心内伤。风雨蹶拔者矣。总言今日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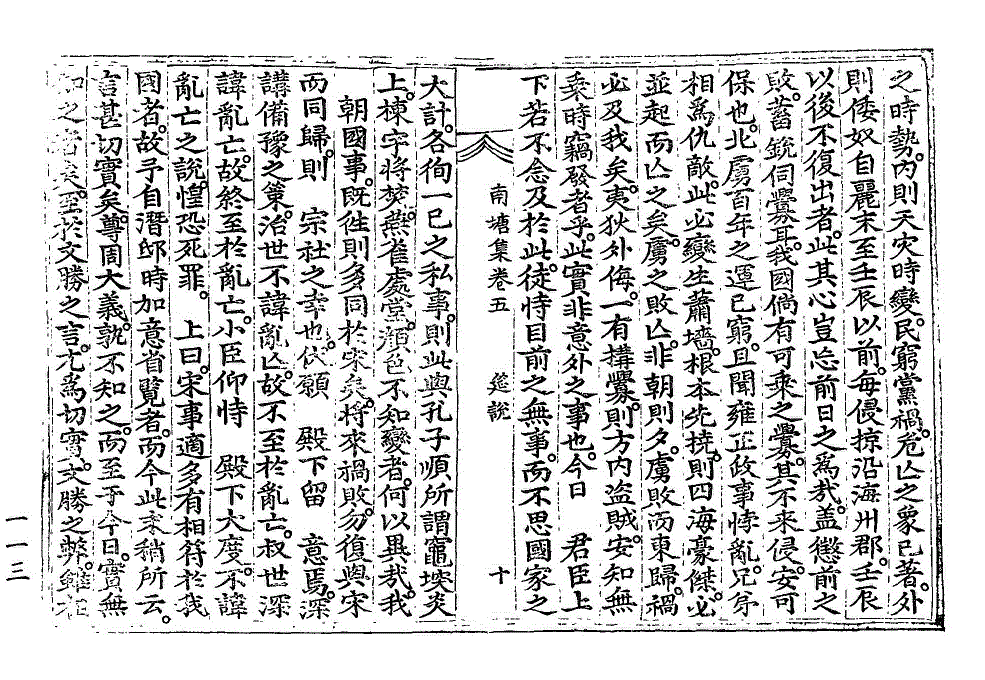 之时势。内则天灾时变。民穷党祸。危亡之象已著。外则倭奴自丽末至壬辰以前。每侵掠沿海州郡。壬辰以后不复出者。此其心岂忘前日之为哉。盖惩前之败。蓄锐伺衅耳。我国倘有可乘之衅。其不来侵。安可保也。北虏百年之运已穷。且闻雍正政事悖乱。兄弟相为仇敌。此必变生萧墙。根本先挠。则四海豪杰。必并起而亡之矣。虏之败亡。非朝则夕。虏败而东归。祸必及我矣。夷狄外侮。一有构衅。则方内盗贼。安知无乘时窃发者乎。此实非意外之事也。今日 君臣上下若不念及于此。徒恃目前之无事。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各徇一己之私事。则此与孔子顺所谓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处堂。颜色不知变者。何以异哉。我 朝国事。既往则多同于宋矣。将来祸败。勿复与宋而同归。则 宗社之幸也。伏愿 殿下留 意焉。深讲备豫之策。治世不讳乱亡。故不至于乱亡。叔世深讳乱亡。故终至于乱亡。小臣仰恃 殿下大度。不讳乱亡之说。惶恐死罪。 上曰。宋事适多有相符于我国者。故予自潜邸时加意省览者。而今此末稍所云。言甚切实矣。尊周大义。孰不知之。而至于今日。实无知之者矣。至于文胜之言。尤为切实。文胜之弊。虽在
之时势。内则天灾时变。民穷党祸。危亡之象已著。外则倭奴自丽末至壬辰以前。每侵掠沿海州郡。壬辰以后不复出者。此其心岂忘前日之为哉。盖惩前之败。蓄锐伺衅耳。我国倘有可乘之衅。其不来侵。安可保也。北虏百年之运已穷。且闻雍正政事悖乱。兄弟相为仇敌。此必变生萧墙。根本先挠。则四海豪杰。必并起而亡之矣。虏之败亡。非朝则夕。虏败而东归。祸必及我矣。夷狄外侮。一有构衅。则方内盗贼。安知无乘时窃发者乎。此实非意外之事也。今日 君臣上下若不念及于此。徒恃目前之无事。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各徇一己之私事。则此与孔子顺所谓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处堂。颜色不知变者。何以异哉。我 朝国事。既往则多同于宋矣。将来祸败。勿复与宋而同归。则 宗社之幸也。伏愿 殿下留 意焉。深讲备豫之策。治世不讳乱亡。故不至于乱亡。叔世深讳乱亡。故终至于乱亡。小臣仰恃 殿下大度。不讳乱亡之说。惶恐死罪。 上曰。宋事适多有相符于我国者。故予自潜邸时加意省览者。而今此末稍所云。言甚切实矣。尊周大义。孰不知之。而至于今日。实无知之者矣。至于文胜之言。尤为切实。文胜之弊。虽在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4H 页
 前亦岂无之。而未有如近来之甚矣。今观所陈。实多常虑之所不及者。予甚嘉之。向者多有所陈戒者。故其后药房入诊时。又为称善矣。予虽无知人之明。岂无一二分之知乎。古之人过贤者之闾则必式。予今日得闻格言。讵无中心之式乎。当猛省而服膺焉。元震曰。所达肤浅。而 奖纳如是。不胜惶恐感激。诸臣达文义云云。 上曰。钦宗之往青城。无计之甚者。而况劝之行乎。李若水之节则可尚。而其所计虑。有不逮者矣。经筵官之意何如。元震对曰。诸臣所达皆得。而 上教亦至当矣。古人亦有言其若水以劝行误事之故。感愤成节者矣。承旨曰云云。 上曰。其言好矣。元震曰。承旨所达观史之法甚好。史籍极其浩穰。小小等处。何可尽为加察而记有哉。当观其紧要处而鉴戒之耳。以今日所论宋事而言之。则存亡成败。只关于和之一字矣。两国势敌。而欲和者或因其厌兵。或惧其败事。此固出于诚实而可与和矣。若两国强弱势悬。而强者求和。此其心岂出于诚实哉。力之所可取而不取。虽五霸亦不能为之矣。况夷狄及于其力之所可取而不取。欲与和而俾存之乎。金虏之以和为言者。盖恐勤王之师日集。又恐宋人奋发而
前亦岂无之。而未有如近来之甚矣。今观所陈。实多常虑之所不及者。予甚嘉之。向者多有所陈戒者。故其后药房入诊时。又为称善矣。予虽无知人之明。岂无一二分之知乎。古之人过贤者之闾则必式。予今日得闻格言。讵无中心之式乎。当猛省而服膺焉。元震曰。所达肤浅。而 奖纳如是。不胜惶恐感激。诸臣达文义云云。 上曰。钦宗之往青城。无计之甚者。而况劝之行乎。李若水之节则可尚。而其所计虑。有不逮者矣。经筵官之意何如。元震对曰。诸臣所达皆得。而 上教亦至当矣。古人亦有言其若水以劝行误事之故。感愤成节者矣。承旨曰云云。 上曰。其言好矣。元震曰。承旨所达观史之法甚好。史籍极其浩穰。小小等处。何可尽为加察而记有哉。当观其紧要处而鉴戒之耳。以今日所论宋事而言之。则存亡成败。只关于和之一字矣。两国势敌。而欲和者或因其厌兵。或惧其败事。此固出于诚实而可与和矣。若两国强弱势悬。而强者求和。此其心岂出于诚实哉。力之所可取而不取。虽五霸亦不能为之矣。况夷狄及于其力之所可取而不取。欲与和而俾存之乎。金虏之以和为言者。盖恐勤王之师日集。又恐宋人奋发而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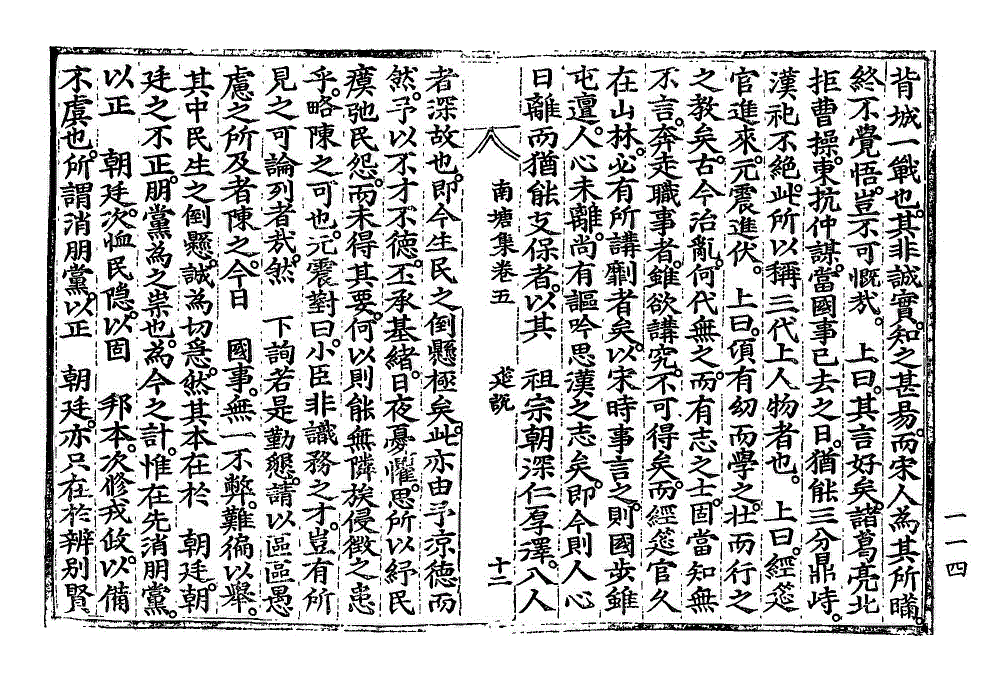 背城一战也。其非诚实。知之甚易。而宋人为其所瞒。终不觉悟。岂不可慨哉。 上曰。其言好矣。诸葛亮北拒曹操。东抗仲谋。当国事已去之日。犹能三分鼎峙。汉祀不绝。此所以称三代上人物者也。 上曰。经筵官进来。元震进伏。 上曰。顷有幼而学之。壮而行之之教矣。古今治乱。何代无之。而有志之士。固当知无不言。奔走职事者。虽欲讲究。不可得矣。而经筵官久在山林。必有所讲劘者矣。以宋时事言之。则国步虽屯邅。人心未离。尚有讴吟思汉之志矣。即今则人心日离而犹能支保者。以其 祖宗朝深仁厚泽。入人者深故也。即今生民之倒悬极矣。此亦由予凉德而然。予以不才不德。丕承基绪。日夜忧惧。思所以纾民瘼弛民怨。而未得其要。何以则能无邻族侵徵之患乎。略陈之可也。元震对曰。小臣非识务之才。岂有所见之可论列者哉。然 下询若是勤恳。请以区区愚虑之所及者陈之。今日 国事。无一不弊。难遍以举。其中民生之倒悬。诚为切急。然其本在于 朝廷。朝廷之不正。朋党为之祟也。为今之计。惟在先消朋党。以正 朝廷。次恤民隐。以固 邦本。次修戎政。以备不虞也。所谓消朋党。以正 朝廷。亦只在于辨别贤
背城一战也。其非诚实。知之甚易。而宋人为其所瞒。终不觉悟。岂不可慨哉。 上曰。其言好矣。诸葛亮北拒曹操。东抗仲谋。当国事已去之日。犹能三分鼎峙。汉祀不绝。此所以称三代上人物者也。 上曰。经筵官进来。元震进伏。 上曰。顷有幼而学之。壮而行之之教矣。古今治乱。何代无之。而有志之士。固当知无不言。奔走职事者。虽欲讲究。不可得矣。而经筵官久在山林。必有所讲劘者矣。以宋时事言之。则国步虽屯邅。人心未离。尚有讴吟思汉之志矣。即今则人心日离而犹能支保者。以其 祖宗朝深仁厚泽。入人者深故也。即今生民之倒悬极矣。此亦由予凉德而然。予以不才不德。丕承基绪。日夜忧惧。思所以纾民瘼弛民怨。而未得其要。何以则能无邻族侵徵之患乎。略陈之可也。元震对曰。小臣非识务之才。岂有所见之可论列者哉。然 下询若是勤恳。请以区区愚虑之所及者陈之。今日 国事。无一不弊。难遍以举。其中民生之倒悬。诚为切急。然其本在于 朝廷。朝廷之不正。朋党为之祟也。为今之计。惟在先消朋党。以正 朝廷。次恤民隐。以固 邦本。次修戎政。以备不虞也。所谓消朋党。以正 朝廷。亦只在于辨别贤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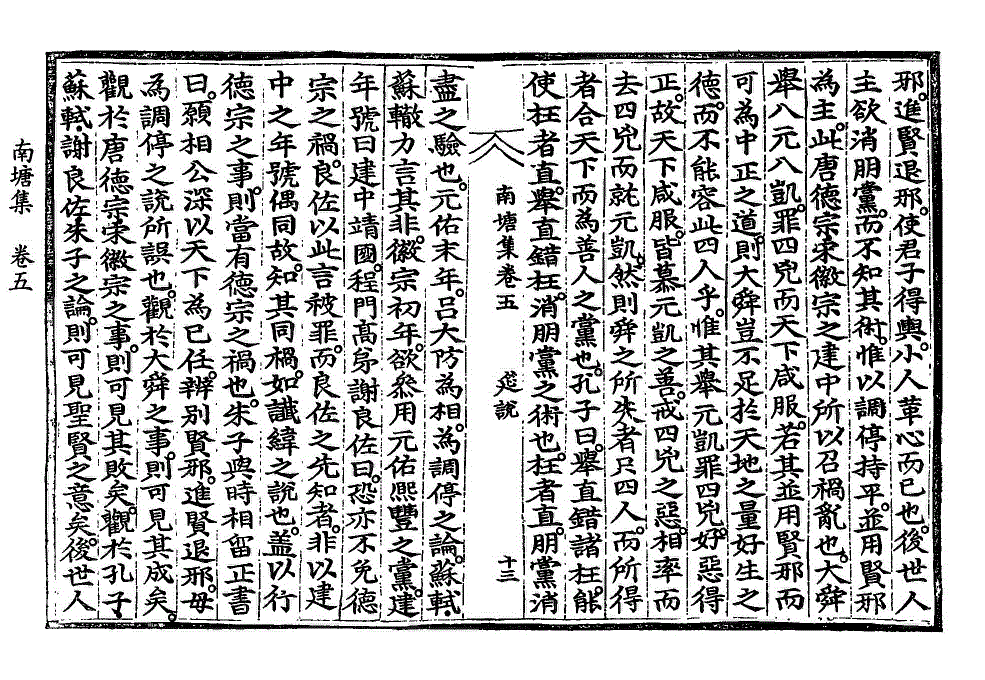 邪。进贤退邪。使君子得舆。小人革心而已也。后世人主欲消朋党。而不知其术。惟以调停持平。并用贤邪为主。此唐德宗,宋徽宗之建中所以召祸乱也。大舜举八元八凯。罪四凶而天下咸服。若其并用贤邪而可为中正之道。则大舜岂不足于天地之量好生之德。而不能容此四人乎。惟其举元凯罪四凶。好恶得正。故天下咸服。皆慕元凯之善。戒四凶之恶。相率而去四凶而就元凯。然则舜之所失者只四人。而所得者合天下而为善人之党也。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枉。消朋党之术也。枉者直。朋党消尽之验也。元佑末年。吕大防为相。为调停之论。苏轼,苏辙力言其非。徽宗初年。欲参用元佑熙丰之党。建年号曰建中靖国。程门高弟谢良佐曰。恐亦不免德宗之祸。良佐以此言被罪。而良佐之先知者。非以建中之年号偶同故。知其同祸。如谶纬之说也。盖以行德宗之事。则当有德宗之祸也。朱子与时相留正书曰。愿相公深以天下为己任。辨别贤邪。进贤退邪。毋为调停之说所误也。观于大舜之事。则可见其成矣。观于唐德宗,宋徽宗之事。则可见其败矣。观于孔子,苏轼,谢良佐,朱子之论。则可见圣贤之意矣。后世人
邪。进贤退邪。使君子得舆。小人革心而已也。后世人主欲消朋党。而不知其术。惟以调停持平。并用贤邪为主。此唐德宗,宋徽宗之建中所以召祸乱也。大舜举八元八凯。罪四凶而天下咸服。若其并用贤邪而可为中正之道。则大舜岂不足于天地之量好生之德。而不能容此四人乎。惟其举元凯罪四凶。好恶得正。故天下咸服。皆慕元凯之善。戒四凶之恶。相率而去四凶而就元凯。然则舜之所失者只四人。而所得者合天下而为善人之党也。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枉。消朋党之术也。枉者直。朋党消尽之验也。元佑末年。吕大防为相。为调停之论。苏轼,苏辙力言其非。徽宗初年。欲参用元佑熙丰之党。建年号曰建中靖国。程门高弟谢良佐曰。恐亦不免德宗之祸。良佐以此言被罪。而良佐之先知者。非以建中之年号偶同故。知其同祸。如谶纬之说也。盖以行德宗之事。则当有德宗之祸也。朱子与时相留正书曰。愿相公深以天下为己任。辨别贤邪。进贤退邪。毋为调停之说所误也。观于大舜之事。则可见其成矣。观于唐德宗,宋徽宗之事。则可见其败矣。观于孔子,苏轼,谢良佐,朱子之论。则可见圣贤之意矣。后世人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5L 页
 君。又以为举朝分党。世传其论。一边岂尽君子。一边岂尽小人也。此则似然而甚不然者。凡事本领一差。末流益谬。故君子党中有小人。而小人党中。决无君子也。是以唐之朋党。李德裕之党。固有小人。而牛僧孺之党。未闻有君子也。宋之朋党。元佑之党。固有小人。而熙丰之党。未闻有君子也。故圣王之用人。必使君子操柄而小人为役。使小人其优者革心而从善。其甚者亦革面而不敢为恶矣。此则朋党之所以无而朝廷之所以正也。至于恤民隐。以固 邦本。修戎政。以备不虞。节目非一二端。措置亦各有术。小臣固无知识。亦不敢以言语烦达。大要 殿下正心立极。任贤使能。则智者能谋事。勇者能断事。仁者能成事。而国家事无所难为者矣。 上曰。其言好矣。造次所陈。极为要约。其不孤予意可知也。予岂有疑其朋党之心乎。举元凯诛四凶而合天下为善人之党云者。极为切实。予心今日后始晓然矣。元震对曰。臣闻知之非难。行之为难。臣言固不足采。凡于廷臣之言。如知其善。断然行之。不然则无贵于知其善矣。 上曰。其言尤好。当留意焉。 上曰。户布结布口钱游布等事。庙堂之讲究揣摩者久矣。我国之三税。异于古者。
君。又以为举朝分党。世传其论。一边岂尽君子。一边岂尽小人也。此则似然而甚不然者。凡事本领一差。末流益谬。故君子党中有小人。而小人党中。决无君子也。是以唐之朋党。李德裕之党。固有小人。而牛僧孺之党。未闻有君子也。宋之朋党。元佑之党。固有小人。而熙丰之党。未闻有君子也。故圣王之用人。必使君子操柄而小人为役。使小人其优者革心而从善。其甚者亦革面而不敢为恶矣。此则朋党之所以无而朝廷之所以正也。至于恤民隐。以固 邦本。修戎政。以备不虞。节目非一二端。措置亦各有术。小臣固无知识。亦不敢以言语烦达。大要 殿下正心立极。任贤使能。则智者能谋事。勇者能断事。仁者能成事。而国家事无所难为者矣。 上曰。其言好矣。造次所陈。极为要约。其不孤予意可知也。予岂有疑其朋党之心乎。举元凯诛四凶而合天下为善人之党云者。极为切实。予心今日后始晓然矣。元震对曰。臣闻知之非难。行之为难。臣言固不足采。凡于廷臣之言。如知其善。断然行之。不然则无贵于知其善矣。 上曰。其言尤好。当留意焉。 上曰。户布结布口钱游布等事。庙堂之讲究揣摩者久矣。我国之三税。异于古者。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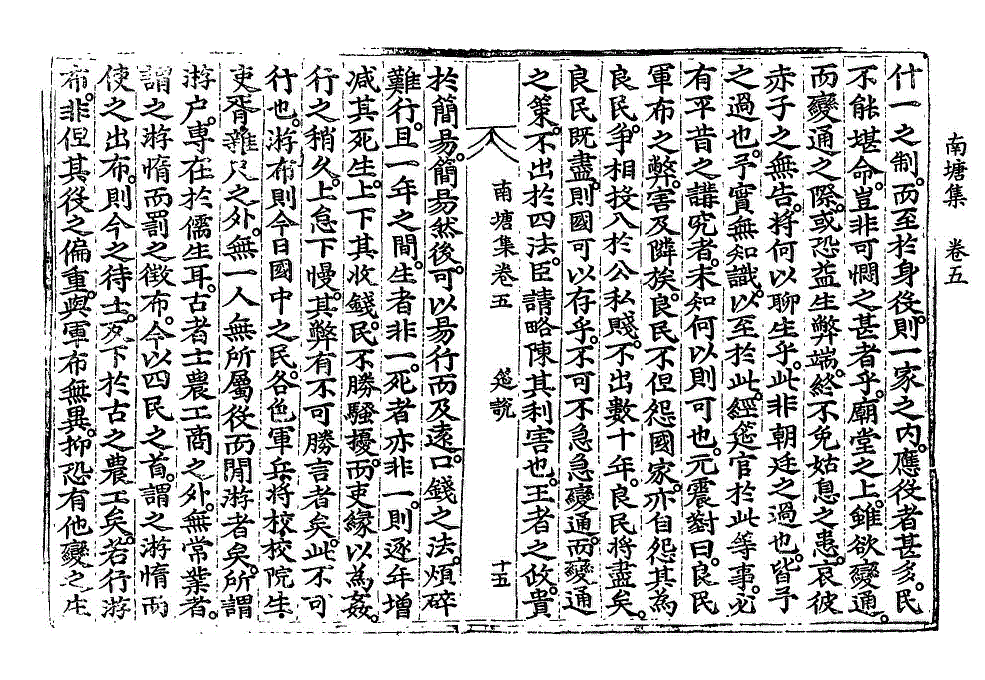 什一之制。而至于身役。则一家之内。应役者甚多。民不能堪命。岂非可悯之甚者乎。庙堂之上。虽欲变通。而变通之际。或恐益生弊端。终不免姑息之患。哀彼赤子之无告。将何以聊生乎。此非朝廷之过也。皆予之过也。予实无知识。以至于此。经筵官于此等事。必有平昔之讲究者。未知何以则可也。元震对曰。良民军布之弊。害及邻族。良民不但怨国家。亦自怨其为良民。争相投入于公私贱。不出数十年。良民将尽矣。良民既尽。则国可以存乎。不可不急急变通。而变通之策。不出于四法。臣请略陈其利害也。王者之政。贵于简易。简易然后。可以易行而及远。口钱之法。烦碎难行。且一年之间。生者非一。死者亦非一。则逐年增减其死生。上下其收钱。民不胜骚扰。而吏缘以为奸。行之稍久。上怠下慢。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不可行也。游布则今日国中之民。各色军兵,将校,校院生,吏胥,杂尺之外。无一人无所属役而閒游者矣。所谓游户。专在于儒生耳。古者士农工商之外。无常业者。谓之游惰而罚之徵布。今以四民之首。谓之游惰而使之出布。则今之待士。反下于古之农工矣。若行游布。非但其役之偏重。与军布无异。抑恐有他变之生
什一之制。而至于身役。则一家之内。应役者甚多。民不能堪命。岂非可悯之甚者乎。庙堂之上。虽欲变通。而变通之际。或恐益生弊端。终不免姑息之患。哀彼赤子之无告。将何以聊生乎。此非朝廷之过也。皆予之过也。予实无知识。以至于此。经筵官于此等事。必有平昔之讲究者。未知何以则可也。元震对曰。良民军布之弊。害及邻族。良民不但怨国家。亦自怨其为良民。争相投入于公私贱。不出数十年。良民将尽矣。良民既尽。则国可以存乎。不可不急急变通。而变通之策。不出于四法。臣请略陈其利害也。王者之政。贵于简易。简易然后。可以易行而及远。口钱之法。烦碎难行。且一年之间。生者非一。死者亦非一。则逐年增减其死生。上下其收钱。民不胜骚扰。而吏缘以为奸。行之稍久。上怠下慢。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不可行也。游布则今日国中之民。各色军兵,将校,校院生,吏胥,杂尺之外。无一人无所属役而閒游者矣。所谓游户。专在于儒生耳。古者士农工商之外。无常业者。谓之游惰而罚之徵布。今以四民之首。谓之游惰而使之出布。则今之待士。反下于古之农工矣。若行游布。非但其役之偏重。与军布无异。抑恐有他变之生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6L 页
 也。此不可行也。结布则贫富似乎均役。而利害猝乍难见。故人多称便。而其害深远。行之。必为亡国之政也。臣居在乡曲。详知土地之所出。薄田一结之地。应贡税大同杂役新旧官刷马之价。田役固已甚重矣。又加以结布。则一结当不下一匹矣。民耕一结之地。输此归官。岂复有所馀可以自食者乎。民之耕田。计其公家之所输及其种子之本,耕作之劳。更无馀资可以自食。则必不耕其田矣。良田虽或不废。薄田必皆陈弃。我国土地薄者过半。弃其一半之田。以闭生财之源。而上下用财自如其旧。则其可支保乎。此外弊端。虽不能尽达。而又非一二矣。此决不可行也。臣谓四法之中。户布最便。可行后世。作法。当依仿古意而行之。孟子言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即周礼所谓一夫百亩之税也。布缕之征。即周礼所谓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力役之征。即周礼所谓一家力役之征也。唐之租庸调。亦本于此。此三者之役。古之圣王。并行不悖。而不以此废彼者也。我国田役则均矣。而身役不均。户役则全阙矣。我国民户之数。较之出布之军。其数十馀倍矣。上自公卿。下至贱隶。有户者皆出布。一人之役。十馀人分应。则役轻
也。此不可行也。结布则贫富似乎均役。而利害猝乍难见。故人多称便。而其害深远。行之。必为亡国之政也。臣居在乡曲。详知土地之所出。薄田一结之地。应贡税大同杂役新旧官刷马之价。田役固已甚重矣。又加以结布。则一结当不下一匹矣。民耕一结之地。输此归官。岂复有所馀可以自食者乎。民之耕田。计其公家之所输及其种子之本,耕作之劳。更无馀资可以自食。则必不耕其田矣。良田虽或不废。薄田必皆陈弃。我国土地薄者过半。弃其一半之田。以闭生财之源。而上下用财自如其旧。则其可支保乎。此外弊端。虽不能尽达。而又非一二矣。此决不可行也。臣谓四法之中。户布最便。可行后世。作法。当依仿古意而行之。孟子言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即周礼所谓一夫百亩之税也。布缕之征。即周礼所谓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力役之征。即周礼所谓一家力役之征也。唐之租庸调。亦本于此。此三者之役。古之圣王。并行不悖。而不以此废彼者也。我国田役则均矣。而身役不均。户役则全阙矣。我国民户之数。较之出布之军。其数十馀倍矣。上自公卿。下至贱隶。有户者皆出布。一人之役。十馀人分应。则役轻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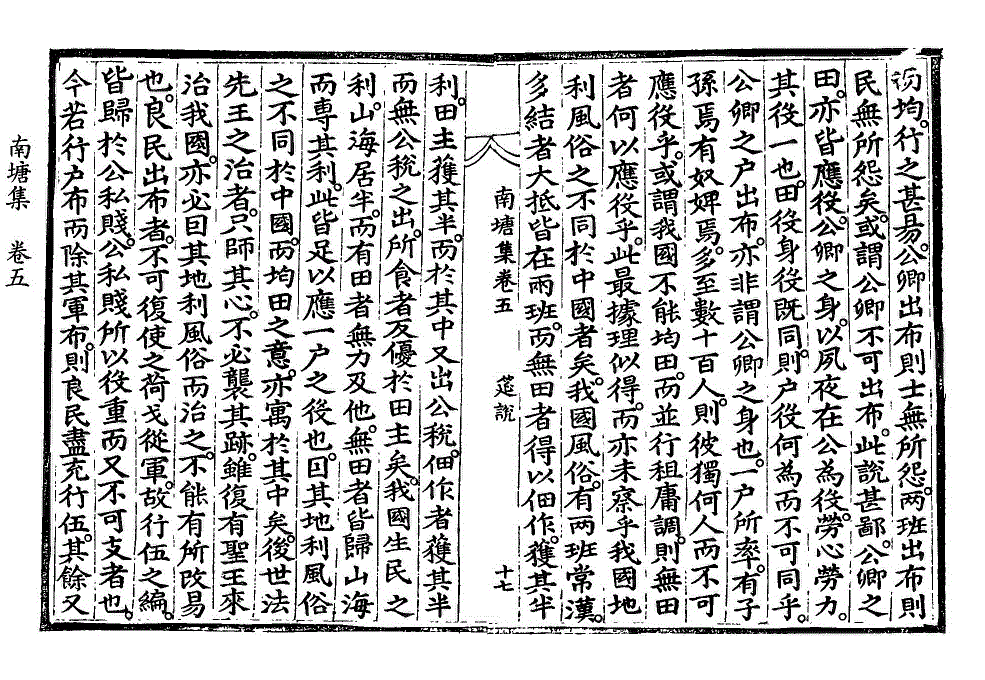 而均。行之甚易。公卿出布则士无所怨。两班出布则民无所怨矣。或谓公卿不可出布。此说甚鄙。公卿之田。亦皆应役。公卿之身。以夙夜在公为役。劳心劳力。其役一也。田役身役既同。则户役何为而不可同乎。公卿之户出布。亦非谓公卿之身也。一户所率。有子孙焉有奴婢焉。多至数十百人。则彼独何人而不可应役乎。或谓我国不能均田。而并行租庸调。则无田者何以应役乎。此最据理似得。而亦未察乎我国地利风俗之不同于中国者矣。我国风俗。有两班常汉。多结者大抵皆在两班。而无田者得以佃作。获其半利。田主获其半。而于其中又出公税。佃作者获其半而无公税之出。所食者反优于田主矣。我国生民之利。山海居半。而有田者无力及他。无田者皆归山海而专其利。此皆足以应一户之役也。因其地利风俗之不同于中国。而均田之意。亦寓于其中矣。后世法先王之治者。只师其心。不必袭其迹。虽复有圣王来治我国。亦必因其地利风俗而治之。不能有所改易也。良民出布者。不可复使之荷戈从军。故行伍之编。皆归于公私贱。公私贱所以役重而又不可支者也。今若行户布而除其军布。则良民尽充行伍。其馀又
而均。行之甚易。公卿出布则士无所怨。两班出布则民无所怨矣。或谓公卿不可出布。此说甚鄙。公卿之田。亦皆应役。公卿之身。以夙夜在公为役。劳心劳力。其役一也。田役身役既同。则户役何为而不可同乎。公卿之户出布。亦非谓公卿之身也。一户所率。有子孙焉有奴婢焉。多至数十百人。则彼独何人而不可应役乎。或谓我国不能均田。而并行租庸调。则无田者何以应役乎。此最据理似得。而亦未察乎我国地利风俗之不同于中国者矣。我国风俗。有两班常汉。多结者大抵皆在两班。而无田者得以佃作。获其半利。田主获其半。而于其中又出公税。佃作者获其半而无公税之出。所食者反优于田主矣。我国生民之利。山海居半。而有田者无力及他。无田者皆归山海而专其利。此皆足以应一户之役也。因其地利风俗之不同于中国。而均田之意。亦寓于其中矣。后世法先王之治者。只师其心。不必袭其迹。虽复有圣王来治我国。亦必因其地利风俗而治之。不能有所改易也。良民出布者。不可复使之荷戈从军。故行伍之编。皆归于公私贱。公私贱所以役重而又不可支者也。今若行户布而除其军布。则良民尽充行伍。其馀又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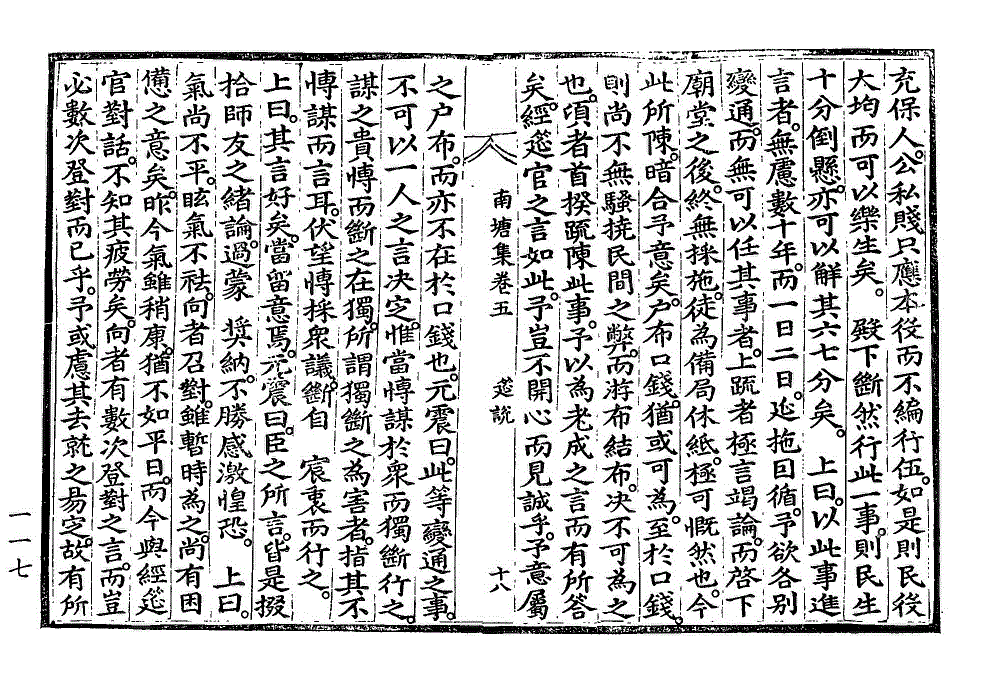 充保人。公私贱只应本役而不编行伍。如是则民役大均而可以乐生矣。 殿下断然行此一事。则民生十分倒悬。亦可以解其六七分矣。 上曰。以此事进言者。无虑数十年。而一日二日。延拖因循。予欲各别变通。而无可以任其事者。上疏者极言竭论。而启下庙堂之后。终无采施。徒为备局休纸。极可慨然也。今此所陈。暗合予意矣。户布口钱。犹或可为。至于口钱。则尚不无骚挠民间之弊。而游布结布。决不可为之也。顷者首揆疏陈此事。予以为老成之言而有所答矣。经筵官之言如此。予岂不开心而见诚乎。予意属之户布。而亦不在于口钱也。元震曰。此等变通之事。不可以一人之言决定。惟当博谋于众而独断行之。谋之贵博而断之在独。所谓独断之为害者。指其不博谋而言耳。伏望博采众议。断自 宸衷而行之。 上曰。其言好矣。当留意焉。元震曰。臣之所言。皆是掇拾师友之绪论。过蒙 奖纳。不胜感激惶恐。 上曰。气尚不平。眩气不祛。向者召对。虽暂时为之。尚有困惫之意矣。昨今气虽稍康。犹不如平日。而今与经筵官对话。不知其疲劳矣。向者有数次登对之言。而岂必数次登对而已乎。予或虑其去就之易定。故有所
充保人。公私贱只应本役而不编行伍。如是则民役大均而可以乐生矣。 殿下断然行此一事。则民生十分倒悬。亦可以解其六七分矣。 上曰。以此事进言者。无虑数十年。而一日二日。延拖因循。予欲各别变通。而无可以任其事者。上疏者极言竭论。而启下庙堂之后。终无采施。徒为备局休纸。极可慨然也。今此所陈。暗合予意矣。户布口钱。犹或可为。至于口钱。则尚不无骚挠民间之弊。而游布结布。决不可为之也。顷者首揆疏陈此事。予以为老成之言而有所答矣。经筵官之言如此。予岂不开心而见诚乎。予意属之户布。而亦不在于口钱也。元震曰。此等变通之事。不可以一人之言决定。惟当博谋于众而独断行之。谋之贵博而断之在独。所谓独断之为害者。指其不博谋而言耳。伏望博采众议。断自 宸衷而行之。 上曰。其言好矣。当留意焉。元震曰。臣之所言。皆是掇拾师友之绪论。过蒙 奖纳。不胜感激惶恐。 上曰。气尚不平。眩气不祛。向者召对。虽暂时为之。尚有困惫之意矣。昨今气虽稍康。犹不如平日。而今与经筵官对话。不知其疲劳矣。向者有数次登对之言。而岂必数次登对而已乎。予或虑其去就之易定。故有所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8H 页
 下教矣。自明日 国忌稠叠。且 国祥不远。其间无故日召对时。同入可也。 上又曰。今日召对之早定者。闻经筵官在于门外。故或虑其日暮不及之患故耳。元震对曰。 上教无非小臣之所不敢当者。臣于顷年。供职 陵官。今若处臣以此等职。则臣岂敢辞避乎。至于 侍讲之任。决非可堪。而以是处臣。此臣所以为难于供职。而 圣教过隆如是。惶陨罔措。不知所 达矣。 上曰。勿为过谦可也。俯伏稍间。仍为退出。
下教矣。自明日 国忌稠叠。且 国祥不远。其间无故日召对时。同入可也。 上又曰。今日召对之早定者。闻经筵官在于门外。故或虑其日暮不及之患故耳。元震对曰。 上教无非小臣之所不敢当者。臣于顷年。供职 陵官。今若处臣以此等职。则臣岂敢辞避乎。至于 侍讲之任。决非可堪。而以是处臣。此臣所以为难于供职。而 圣教过隆如是。惶陨罔措。不知所 达矣。 上曰。勿为过谦可也。俯伏稍间。仍为退出。二十七日召对时。讲宋史高宗记。 上曰。前日筵中已言之。经筵官先陈文义。元震对曰。小小文义。有难尽 达。宋金成败得失大机所在。臣请陈之。金虏既破皇城。执二帝。当此之时。藉其兵威之既振。乘中国土崩之势。因据汴京。追击康王。席捲南下。吴越之地。可不血刃取而天下定矣。虏不知出此。立邦昌为帝。付中原于他人。执二帝而北去。其始之来何意也。其终之去亦何意也。虏之不能取天下者。全在于失此机会也。及其康王渡江立国。根本既固。方始来争。何其计之愚也。康王当二帝北行。邦昌僭位。人心怨愤。虏师退归。河北未尽沦陷之时。纠合忠义。奖率遗民。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8L 页
 以缟素为资。先诛邦昌。北击虏师。二帝可还而中原可复矣。康王不知出此。汲汲渡江。窜伏闽中。坐使中原自归于虏。可胜痛恨哉。只有一宗泽固守东京。规恢中原。而左右沮挠。使不得伸志。饮恨而死。尤可恨也。一失事机。后虽用力百倍。终不能成事。事机所在。不可不审。而虽在古事。亦宜深察而鉴戒之也。 上曰。今闻论宋金之事。平日林下读史。可见其不泛矣。承旨罗学川曰。秦桧云云。元震曰。秦桧之主和。实由于高宗之志不在恢复也。秦桧始与马伸,吴给等抗言虏酋请立赵氏。以此被执而去。桧未尝不知名节之可贵也。桧之南还。若见高宗之志在于必复父兄之雠。则桧必迎合其意。以为名节富贵两得之计。而桧深知高宗之意不在复雠。故迎合其意。以为弃名节图富贵之计矣。或谓桧感虏放还之恩。阴为虏地。此则不知小人之情状也。小人之心。虽于君父之恩。犹不知感。临利害而背之。况为虏守信乎。此则必无之理也。高宗前后任用之人。汪,黄,汤思退之徒。皆主和之人也。岂独秦桧哉。人谓秦桧误高宗。臣则谓高宗误秦桧也。高宗之偷安畏怯。忘父兄之雠者。可为千载之戒也。 上曰。其言是矣。唐太宗明察故小人
以缟素为资。先诛邦昌。北击虏师。二帝可还而中原可复矣。康王不知出此。汲汲渡江。窜伏闽中。坐使中原自归于虏。可胜痛恨哉。只有一宗泽固守东京。规恢中原。而左右沮挠。使不得伸志。饮恨而死。尤可恨也。一失事机。后虽用力百倍。终不能成事。事机所在。不可不审。而虽在古事。亦宜深察而鉴戒之也。 上曰。今闻论宋金之事。平日林下读史。可见其不泛矣。承旨罗学川曰。秦桧云云。元震曰。秦桧之主和。实由于高宗之志不在恢复也。秦桧始与马伸,吴给等抗言虏酋请立赵氏。以此被执而去。桧未尝不知名节之可贵也。桧之南还。若见高宗之志在于必复父兄之雠。则桧必迎合其意。以为名节富贵两得之计。而桧深知高宗之意不在复雠。故迎合其意。以为弃名节图富贵之计矣。或谓桧感虏放还之恩。阴为虏地。此则不知小人之情状也。小人之心。虽于君父之恩。犹不知感。临利害而背之。况为虏守信乎。此则必无之理也。高宗前后任用之人。汪,黄,汤思退之徒。皆主和之人也。岂独秦桧哉。人谓秦桧误高宗。臣则谓高宗误秦桧也。高宗之偷安畏怯。忘父兄之雠者。可为千载之戒也。 上曰。其言是矣。唐太宗明察故小人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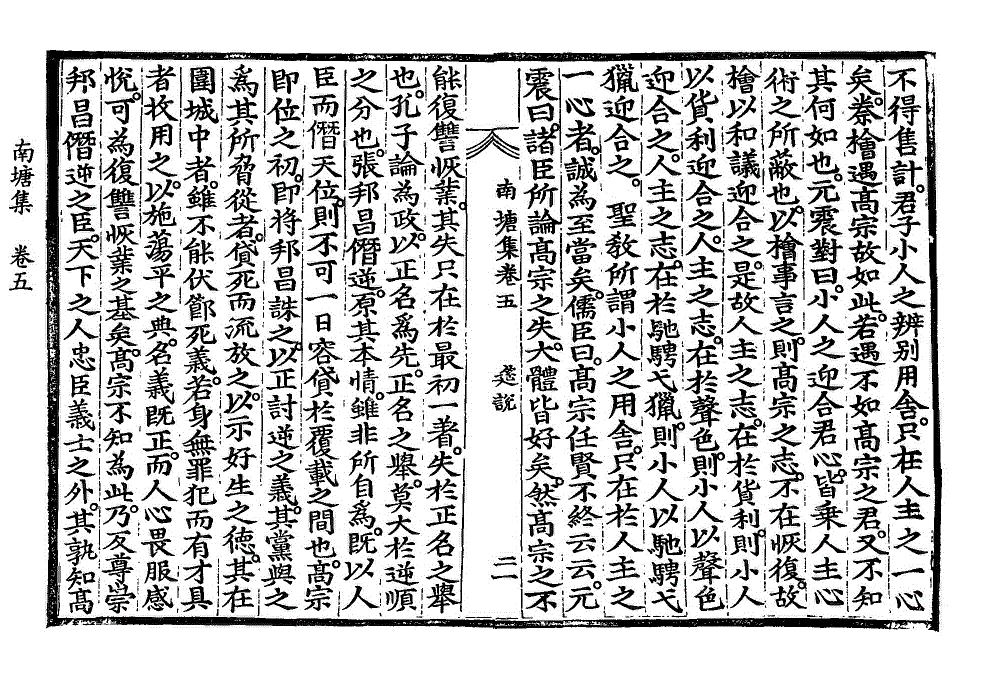 不得售计。君子小人之辨别用舍。只在人主之一心矣。秦桧遇高宗故如此。若遇不如高宗之君。又不知其何如也。元震对曰。小人之迎合君心。皆乘人主心术之所蔽也。以桧事言之。则高宗之志。不在恢复。故桧以和议迎合之。是故人主之志。在于货利。则小人以货利迎合之。人主之志。在于声色。则小人以声色迎合之。人主之志。在于驰骋弋猎。则小人以驰骋弋猎迎合之。 圣教所谓小人之用舍。只在于人主之一心者。诚为至当矣。儒臣曰。高宗任贤不终云云。元震曰。诸臣所论高宗之失。大体皆好矣。然高宗之不能复雠恢业。其失只在于最初一着。失于正名之举也。孔子论为政。以正名为先。正名之举。莫大于逆顺之分也。张邦昌僭逆。原其本情。虽非所自为。既以人臣而僭天位。则不可一日容贷于覆载之间也。高宗即位之初。即将邦昌诛之。以正讨逆之义。其党与之为其所胁从者。贷死而流放之。以示好生之德。其在围城中者。虽不能伏节死义。若身无罪犯而有才具者收用之。以施荡平之典。名义既正。而人心畏服感悦。可为复雠恢业之基矣。高宗不知为此。乃反尊崇邦昌僭逆之臣。天下之人忠臣义士之外。其孰知高
不得售计。君子小人之辨别用舍。只在人主之一心矣。秦桧遇高宗故如此。若遇不如高宗之君。又不知其何如也。元震对曰。小人之迎合君心。皆乘人主心术之所蔽也。以桧事言之。则高宗之志。不在恢复。故桧以和议迎合之。是故人主之志。在于货利。则小人以货利迎合之。人主之志。在于声色。则小人以声色迎合之。人主之志。在于驰骋弋猎。则小人以驰骋弋猎迎合之。 圣教所谓小人之用舍。只在于人主之一心者。诚为至当矣。儒臣曰。高宗任贤不终云云。元震曰。诸臣所论高宗之失。大体皆好矣。然高宗之不能复雠恢业。其失只在于最初一着。失于正名之举也。孔子论为政。以正名为先。正名之举。莫大于逆顺之分也。张邦昌僭逆。原其本情。虽非所自为。既以人臣而僭天位。则不可一日容贷于覆载之间也。高宗即位之初。即将邦昌诛之。以正讨逆之义。其党与之为其所胁从者。贷死而流放之。以示好生之德。其在围城中者。虽不能伏节死义。若身无罪犯而有才具者收用之。以施荡平之典。名义既正。而人心畏服感悦。可为复雠恢业之基矣。高宗不知为此。乃反尊崇邦昌僭逆之臣。天下之人忠臣义士之外。其孰知高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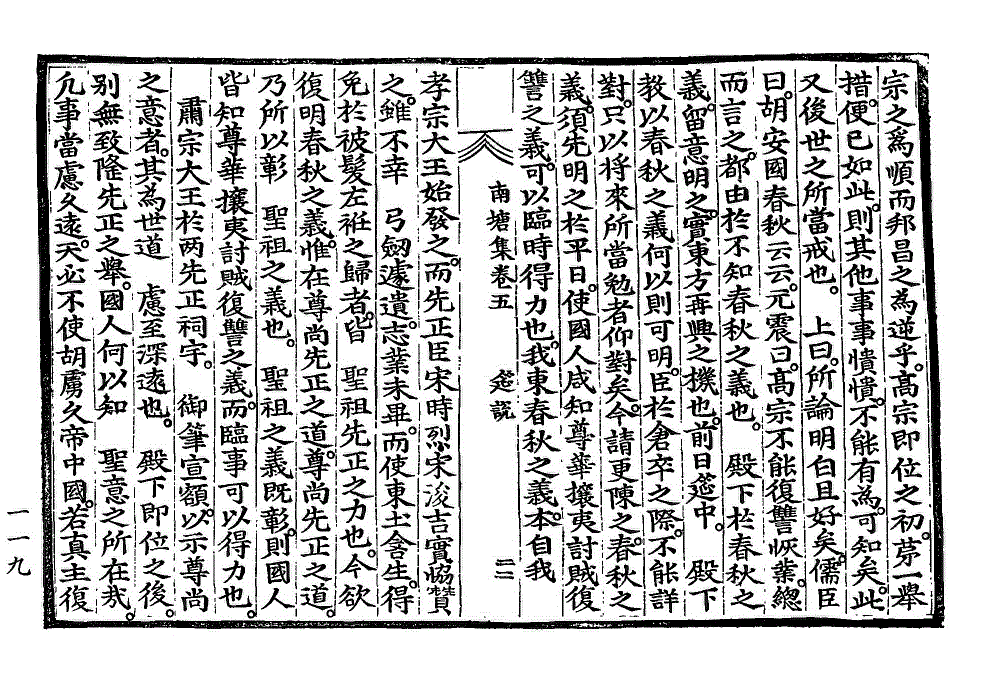 宗之为顺而邦昌之为逆乎。高宗即位之初。第一举措。便已如此。则其他事事愦愦。不能有为。可知矣。此又后世之所当戒也。 上曰。所论明白且好矣。儒臣曰。胡安国春秋云云。元震曰。高宗不能复雠恢业。总而言之。都由于不知春秋之义也。 殿下于春秋之义。留意明之。实东方再兴之机也。前日筵中。 殿下教以春秋之义何以则可明。臣于仓卒之际。不能详对。只以将来所当勉者仰对矣。今请更陈之。春秋之义。须先明之于平日。使国人咸知尊华攘夷讨贼复雠之义。可以临时得力也。我东春秋之义。本自我 孝宗大王始发之。而先正臣宋时烈,宋浚吉实协赞之。虽不幸 弓剑遽遗。志业未毕。而使东土含生。得免于被发左衽之归者。皆 圣祖先正之力也。今欲复明春秋之义。惟在尊尚先正之道。尊尚先正之道。乃所以彰 圣祖之义也。 圣祖之义既彰。则国人皆知尊华攘夷讨贼复雠之义。而临事可以得力也。 肃宗大王于两先正祠宇。 御笔宣额。以示尊尚之意者。其为世道 虑至深远也。 殿下即位之后。别无致隆先正之举。国人何以知 圣意之所在哉。凡事当虑久远。天必不使胡虏久帝中国。若真主复
宗之为顺而邦昌之为逆乎。高宗即位之初。第一举措。便已如此。则其他事事愦愦。不能有为。可知矣。此又后世之所当戒也。 上曰。所论明白且好矣。儒臣曰。胡安国春秋云云。元震曰。高宗不能复雠恢业。总而言之。都由于不知春秋之义也。 殿下于春秋之义。留意明之。实东方再兴之机也。前日筵中。 殿下教以春秋之义何以则可明。臣于仓卒之际。不能详对。只以将来所当勉者仰对矣。今请更陈之。春秋之义。须先明之于平日。使国人咸知尊华攘夷讨贼复雠之义。可以临时得力也。我东春秋之义。本自我 孝宗大王始发之。而先正臣宋时烈,宋浚吉实协赞之。虽不幸 弓剑遽遗。志业未毕。而使东土含生。得免于被发左衽之归者。皆 圣祖先正之力也。今欲复明春秋之义。惟在尊尚先正之道。尊尚先正之道。乃所以彰 圣祖之义也。 圣祖之义既彰。则国人皆知尊华攘夷讨贼复雠之义。而临事可以得力也。 肃宗大王于两先正祠宇。 御笔宣额。以示尊尚之意者。其为世道 虑至深远也。 殿下即位之后。别无致隆先正之举。国人何以知 圣意之所在哉。凡事当虑久远。天必不使胡虏久帝中国。若真主复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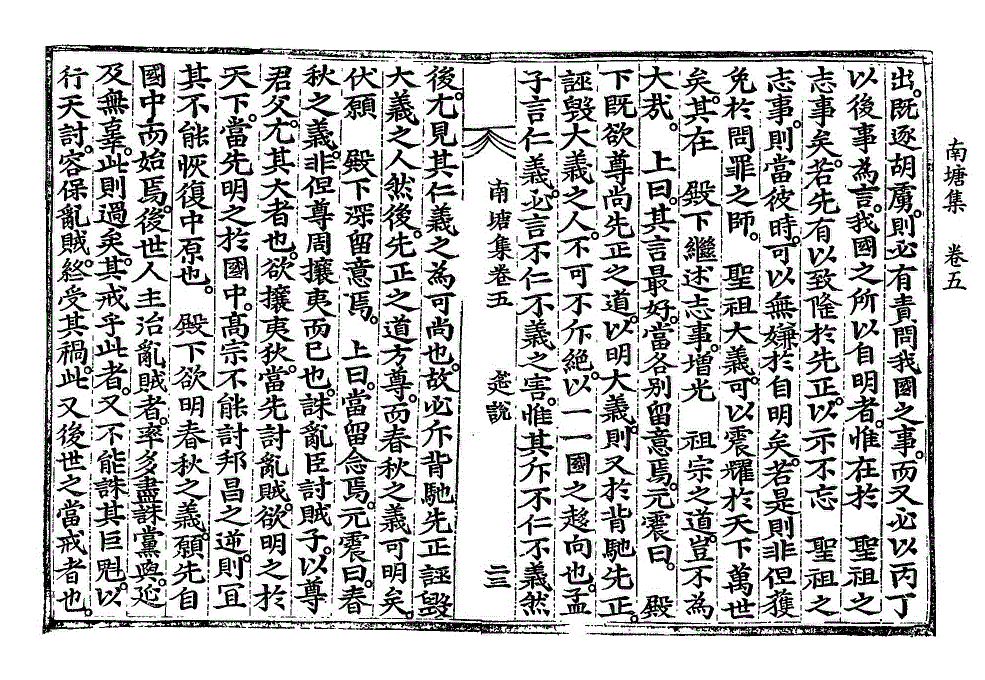 出。既逐胡虏。则必有责问我国之事。而又必以丙丁以后事为言。我国之所以自明者。惟在于 圣祖之志事矣。若先有以致隆于先正。以示不忘 圣祖之志事。则当彼时。可以无嫌于自明矣。若是则非但获免于问罪之师。 圣祖大义。可以震耀于天下万世矣。其在 殿下继述志事。增光 祖宗之道。岂不为大哉。 上曰。其言最好。当各别留意焉。元震曰。 殿下既欲尊尚先正之道。以明大义。则又于背驰先正。诬毁大义之人。不可不斥绝。以一一国之趍向也。孟子言仁义。必言不仁不义之害。惟其斥不仁不义然后。尤见其仁义之为可尚也。故必斥背驰先正诬毁大义之人然后。先正之道方尊。而春秋之义可明矣。伏愿 殿下深留意焉。 上曰。当留念焉。元震曰。春秋之义。非但尊周攘夷而已也。诛乱臣讨贼子。以尊君父。尤其大者也。欲攘夷狄。当先讨乱贼。欲明之于天下。当先明之于国中。高宗不能讨邦昌之逆。则宜其不能恢复中原也。 殿下欲明春秋之义。愿先自国中而始焉。后世人主治乱贼者。率多尽诛党与。延及无辜。此则过矣。其戒乎此者。又不能诛其巨魁。以行天讨。容保乱贼。终受其祸。此又后世之当戒者也。
出。既逐胡虏。则必有责问我国之事。而又必以丙丁以后事为言。我国之所以自明者。惟在于 圣祖之志事矣。若先有以致隆于先正。以示不忘 圣祖之志事。则当彼时。可以无嫌于自明矣。若是则非但获免于问罪之师。 圣祖大义。可以震耀于天下万世矣。其在 殿下继述志事。增光 祖宗之道。岂不为大哉。 上曰。其言最好。当各别留意焉。元震曰。 殿下既欲尊尚先正之道。以明大义。则又于背驰先正。诬毁大义之人。不可不斥绝。以一一国之趍向也。孟子言仁义。必言不仁不义之害。惟其斥不仁不义然后。尤见其仁义之为可尚也。故必斥背驰先正诬毁大义之人然后。先正之道方尊。而春秋之义可明矣。伏愿 殿下深留意焉。 上曰。当留念焉。元震曰。春秋之义。非但尊周攘夷而已也。诛乱臣讨贼子。以尊君父。尤其大者也。欲攘夷狄。当先讨乱贼。欲明之于天下。当先明之于国中。高宗不能讨邦昌之逆。则宜其不能恢复中原也。 殿下欲明春秋之义。愿先自国中而始焉。后世人主治乱贼者。率多尽诛党与。延及无辜。此则过矣。其戒乎此者。又不能诛其巨魁。以行天讨。容保乱贼。终受其祸。此又后世之当戒者也。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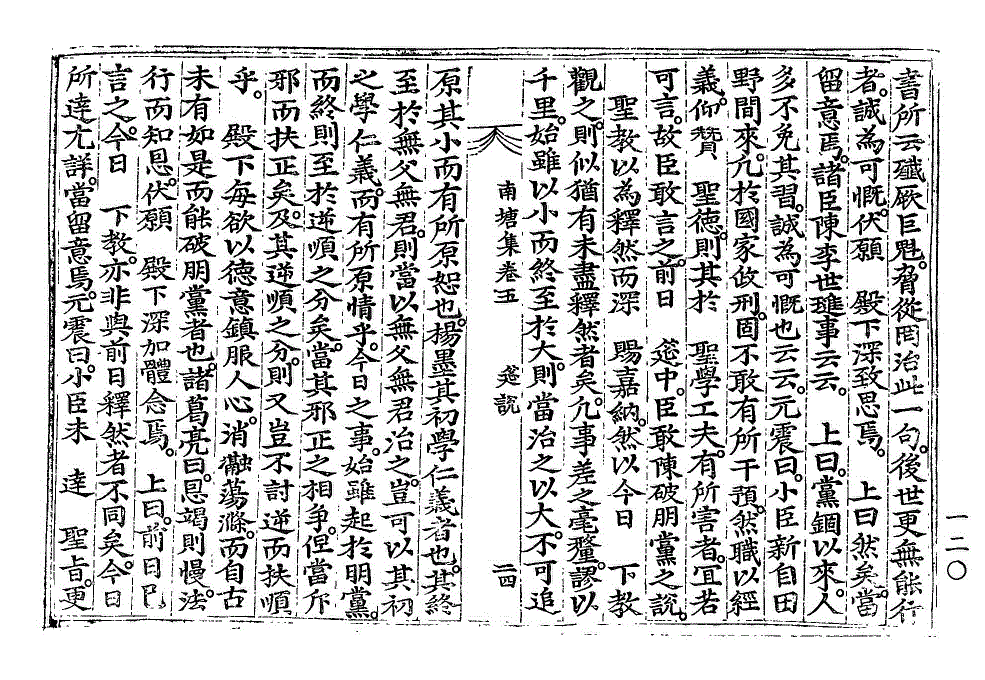 书所云歼厥巨魁。胁从罔治此一句。后世更无能行者。诚为可慨。伏愿 殿下深致思焉。 上曰然矣。当留意焉。诸臣陈李世琎事云云。 上曰。党锢以来。人多不免其习。诚为可慨也云云。元震曰。小臣新自田野间来。凡于国家政刑。固不敢有所干预。然职以经义。仰赞 圣德。则其于 圣学工夫。有所害者。宜若可言。故臣敢言之。前日 筵中。臣敢陈破朋党之说。 圣教以为释然而深 赐嘉纳。然以今日 下教观之。则似犹有未尽释然者矣。凡事差之毫釐。谬以千里。始虽以小而终至于大。则当治之以大。不可追原其小而有所原恕也。杨墨其初学仁义者也。其终至于无父无君。则当以无父无君治之。岂可以其初之学仁义。而有所原情乎。今日之事。始虽起于朋党。而终则至于逆顺之分矣。当其邪正之相争。但当斥邪而扶正矣。及其逆顺之分。则又岂不讨逆而扶顺乎。 殿下每欲以德意镇服人心。消瀜荡涤。而自古未有如是而能破朋党者也。诸葛亮曰。恩竭则慢。法行而知恩。伏愿 殿下深加体念焉。 上曰。前日已言之。今日 下教。亦非与前日释然者不同矣。今日所达尤详。当留意焉。元震曰。小臣未 达 圣旨。更
书所云歼厥巨魁。胁从罔治此一句。后世更无能行者。诚为可慨。伏愿 殿下深致思焉。 上曰然矣。当留意焉。诸臣陈李世琎事云云。 上曰。党锢以来。人多不免其习。诚为可慨也云云。元震曰。小臣新自田野间来。凡于国家政刑。固不敢有所干预。然职以经义。仰赞 圣德。则其于 圣学工夫。有所害者。宜若可言。故臣敢言之。前日 筵中。臣敢陈破朋党之说。 圣教以为释然而深 赐嘉纳。然以今日 下教观之。则似犹有未尽释然者矣。凡事差之毫釐。谬以千里。始虽以小而终至于大。则当治之以大。不可追原其小而有所原恕也。杨墨其初学仁义者也。其终至于无父无君。则当以无父无君治之。岂可以其初之学仁义。而有所原情乎。今日之事。始虽起于朋党。而终则至于逆顺之分矣。当其邪正之相争。但当斥邪而扶正矣。及其逆顺之分。则又岂不讨逆而扶顺乎。 殿下每欲以德意镇服人心。消瀜荡涤。而自古未有如是而能破朋党者也。诸葛亮曰。恩竭则慢。法行而知恩。伏愿 殿下深加体念焉。 上曰。前日已言之。今日 下教。亦非与前日释然者不同矣。今日所达尤详。当留意焉。元震曰。小臣未 达 圣旨。更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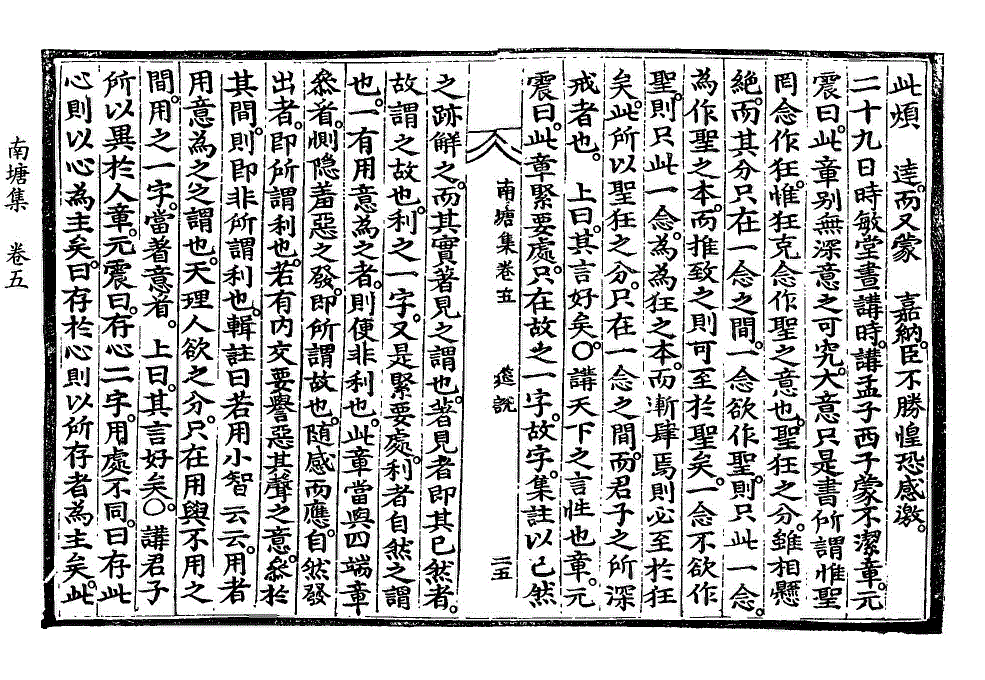 此烦 达。而又蒙 嘉纳。臣不胜惶恐感激。
此烦 达。而又蒙 嘉纳。臣不胜惶恐感激。二十九日时敏堂昼讲时。讲孟子西子蒙不洁章。元震曰。此章别无深意之可究。大意只是书所谓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之意也。圣狂之分。虽相悬绝。而其分只在一念之间。一念欲作圣。则只此一念。为作圣之本。而推致之则可至于圣矣。一念不欲作圣。则只此一念。为为狂之本。而渐肆焉则必至于狂矣。此所以圣狂之分。只在一念之间。而君子之所深戒者也。 上曰。其言好矣。○讲天下之言性也章。元震曰。此章紧要处。只在故之一字。故字。集注以已然之迹解之。而其实著见之谓也。著见者即其已然者。故谓之故也。利之一字。又是紧要处。利者自然之谓也。一有用意为之者。则便非利也。此章当与四端章参看。恻隐羞恶之发。即所谓故也。随感而应。自然发出者。即所谓利也。若有内交要誉恶其声之意。参于其间。则即非所谓利也。辑注曰若用小智云云。用者用意为之之谓也。天理人欲之分。只在用与不用之间。用之一字。当着意看。 上曰。其言好矣。○讲君子所以异于人章。元震曰。存心二字。用处不同。曰存此心则以心为主矣。曰存于心则以所存者为主矣。此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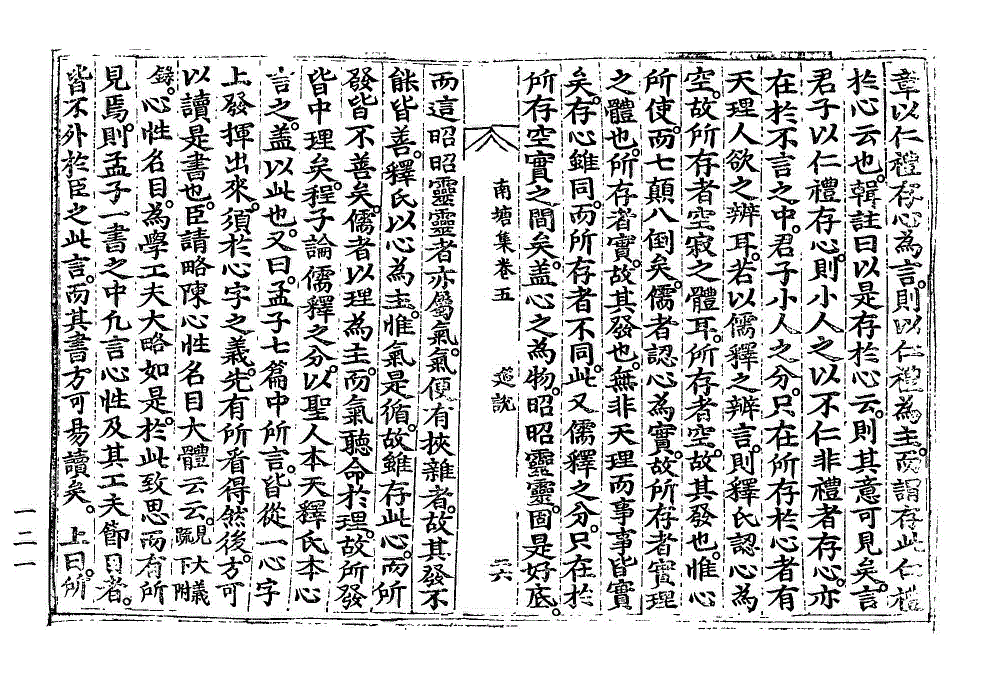 章以仁礼存心为言。则以仁礼为主。而谓存此仁礼于心云也。辑注曰以是存于心云。则其意可见矣。言君子以仁礼存心。则小人之以不仁非礼者存心。亦在于不言之中。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所存于心者有天理人欲之辨耳。若以儒释之辨言。则释氏认心为空。故所存者空寂之体耳。所存者空。故其发也。惟心所使。而七颠八倒矣。儒者认心为实。故所存者实理之体也。所存者实。故其发也。无非天理而事事皆实矣。存心虽同。而所存者不同。此又儒释之分。只在于所存空实之间矣。盖心之为物。昭昭灵灵。固是好底。而这昭昭灵灵者亦属气。气便有挟杂者。故其发不能皆善。释氏以心为主。惟气是循。故虽存此心。而所发皆不善矣。儒者以理为主。而气听命于理。故所发皆中理矣。程子论儒释之分。以圣人本天释氏本心言之。盖以此也。又曰。孟子七篇中所言。皆从一心字上发挥出来。须于心字之义。先有所看得然后。方可以读是书也。臣请略陈心性名目大体云云。(见大义疏下附录。)心性名目。为学工夫大略如是。于此致思而有所见焉。则孟子一书之中凡言心性及其工夫节目者。皆不外于臣之此言。而其书方可易读矣。 上曰。所
章以仁礼存心为言。则以仁礼为主。而谓存此仁礼于心云也。辑注曰以是存于心云。则其意可见矣。言君子以仁礼存心。则小人之以不仁非礼者存心。亦在于不言之中。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所存于心者有天理人欲之辨耳。若以儒释之辨言。则释氏认心为空。故所存者空寂之体耳。所存者空。故其发也。惟心所使。而七颠八倒矣。儒者认心为实。故所存者实理之体也。所存者实。故其发也。无非天理而事事皆实矣。存心虽同。而所存者不同。此又儒释之分。只在于所存空实之间矣。盖心之为物。昭昭灵灵。固是好底。而这昭昭灵灵者亦属气。气便有挟杂者。故其发不能皆善。释氏以心为主。惟气是循。故虽存此心。而所发皆不善矣。儒者以理为主。而气听命于理。故所发皆中理矣。程子论儒释之分。以圣人本天释氏本心言之。盖以此也。又曰。孟子七篇中所言。皆从一心字上发挥出来。须于心字之义。先有所看得然后。方可以读是书也。臣请略陈心性名目大体云云。(见大义疏下附录。)心性名目。为学工夫大略如是。于此致思而有所见焉。则孟子一书之中凡言心性及其工夫节目者。皆不外于臣之此言。而其书方可易读矣。 上曰。所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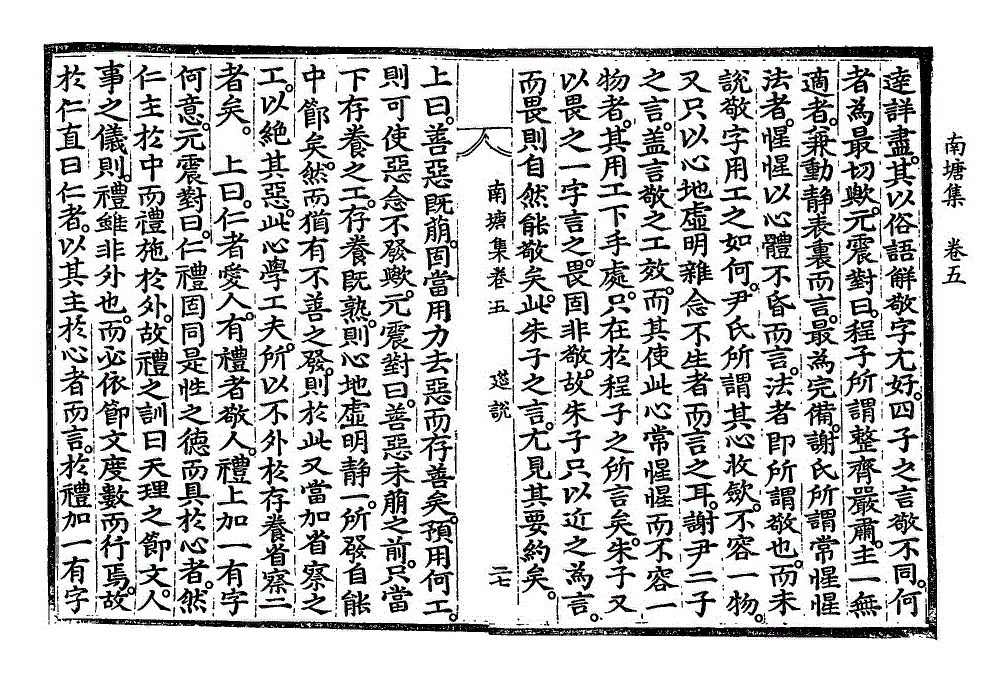 达详尽。其以俗语解敬字尤好。四子之言敬不同。何者为最切欤。元震对曰。程子所谓整齐严肃。主一无适者。兼动静表里而言。最为完备。谢氏所谓常惺惺法者。惺惺以心体不昏而言。法者即所谓敬也。而未说敬字用工之如何。尹氏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又只以心地虚明杂念不生者而言之耳。谢尹二子之言。盖言敬之工效。而其使此心常惺惺而不容一物者。其用工下手处。只在于程子之所言矣。朱子又以畏之一字言之。畏固非敬。故朱子只以近之为言。而畏则自然能敬矣。此朱子之言。尤见其要约矣。 上曰。善恶既萌。固当用力去恶而存善矣。预用何工。则可使恶念不发欤。元震对曰。善恶未萌之前。只当下存养之工。存养既熟。则心地虚明静一。所发自能中节矣。然而犹有不善之发。则于此又当加省察之工。以绝其恶。此心学工夫。所以不外于存养省察二者矣。 上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礼上加一有字何意。元震对曰。仁礼固同是性之德而具于心者。然仁主于中而礼施于外。故礼之训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礼虽非外也。而必依节文度数而行焉。故于仁直曰仁者。以其主于心者而言。于礼加一有字
达详尽。其以俗语解敬字尤好。四子之言敬不同。何者为最切欤。元震对曰。程子所谓整齐严肃。主一无适者。兼动静表里而言。最为完备。谢氏所谓常惺惺法者。惺惺以心体不昏而言。法者即所谓敬也。而未说敬字用工之如何。尹氏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又只以心地虚明杂念不生者而言之耳。谢尹二子之言。盖言敬之工效。而其使此心常惺惺而不容一物者。其用工下手处。只在于程子之所言矣。朱子又以畏之一字言之。畏固非敬。故朱子只以近之为言。而畏则自然能敬矣。此朱子之言。尤见其要约矣。 上曰。善恶既萌。固当用力去恶而存善矣。预用何工。则可使恶念不发欤。元震对曰。善恶未萌之前。只当下存养之工。存养既熟。则心地虚明静一。所发自能中节矣。然而犹有不善之发。则于此又当加省察之工。以绝其恶。此心学工夫。所以不外于存养省察二者矣。 上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礼上加一有字何意。元震对曰。仁礼固同是性之德而具于心者。然仁主于中而礼施于外。故礼之训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礼虽非外也。而必依节文度数而行焉。故于仁直曰仁者。以其主于心者而言。于礼加一有字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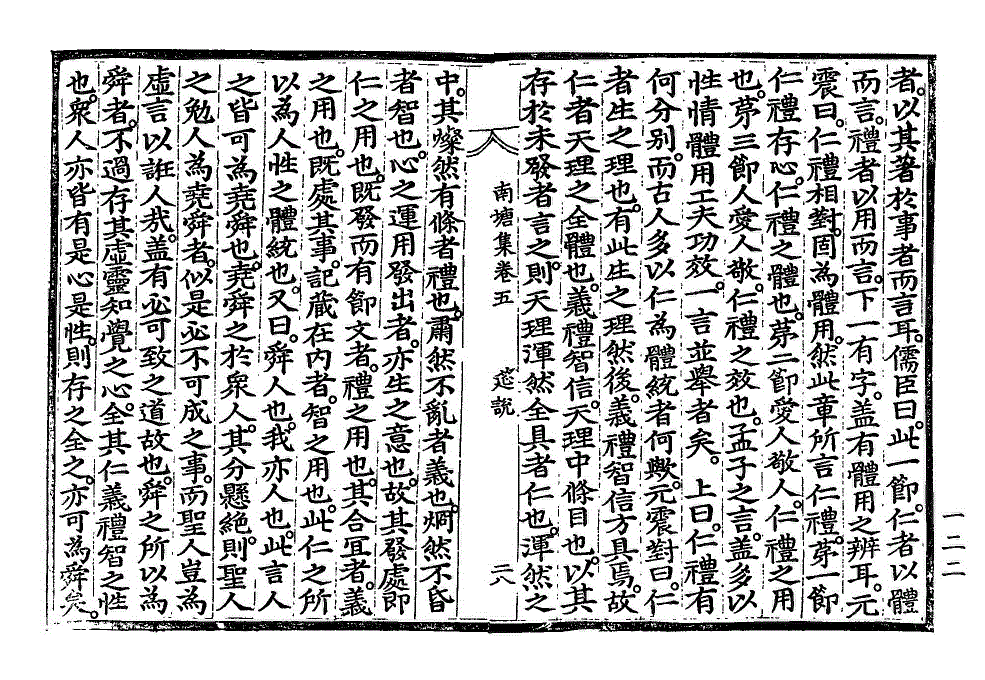 者。以其著于事者而言耳。儒臣曰。此一节。仁者以体而言。礼者以用而言。下一有字。盖有体用之辨耳。元震曰。仁礼相对。固为体用。然此章所言仁礼。第一节仁礼存心。仁礼之体也。第二节爱人敬人。仁礼之用也。第三节人爱人敬。仁礼之效也。孟子之言。盖多以性情体用工夫功效。一言并举者矣。 上曰。仁礼有何分别。而古人多以仁为体统者何欤。元震对曰。仁者生之理也。有此生之理然后。义礼智信方具焉。故仁者天理之全体也。义礼智信。天理中条目也。以其存于未发者言之。则天理浑然全具者仁也。浑然之中。其灿然有条者礼也。肃然不乱者义也。烱然不昏者智也。心之运用发出者。亦生之意也。故其发处即仁之用也。既发而有节文者。礼之用也。其合宜者。义之用也。既处其事。记藏在内者。智之用也。此仁之所以为人性之体统也。又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此言人之皆可为尧舜也。尧舜之于众人。其分悬绝。则圣人之勉人为尧舜者。似是必不可成之事。而圣人岂为虚言以诳人哉。盖有必可致之道故也。舜之所以为舜者。不过存其虚灵知觉之心。全其仁义礼智之性也。众人亦皆有是心是性。则存之全之。亦可为舜矣。
者。以其著于事者而言耳。儒臣曰。此一节。仁者以体而言。礼者以用而言。下一有字。盖有体用之辨耳。元震曰。仁礼相对。固为体用。然此章所言仁礼。第一节仁礼存心。仁礼之体也。第二节爱人敬人。仁礼之用也。第三节人爱人敬。仁礼之效也。孟子之言。盖多以性情体用工夫功效。一言并举者矣。 上曰。仁礼有何分别。而古人多以仁为体统者何欤。元震对曰。仁者生之理也。有此生之理然后。义礼智信方具焉。故仁者天理之全体也。义礼智信。天理中条目也。以其存于未发者言之。则天理浑然全具者仁也。浑然之中。其灿然有条者礼也。肃然不乱者义也。烱然不昏者智也。心之运用发出者。亦生之意也。故其发处即仁之用也。既发而有节文者。礼之用也。其合宜者。义之用也。既处其事。记藏在内者。智之用也。此仁之所以为人性之体统也。又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此言人之皆可为尧舜也。尧舜之于众人。其分悬绝。则圣人之勉人为尧舜者。似是必不可成之事。而圣人岂为虚言以诳人哉。盖有必可致之道故也。舜之所以为舜者。不过存其虚灵知觉之心。全其仁义礼智之性也。众人亦皆有是心是性。则存之全之。亦可为舜矣。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3H 页
 但舜与众人。气质不同。而气质有可变之道。人之身体长短妍媸。固不可变也。至于心之虚明者。则可以变化矣。譬如天地之间。有形质者。皆不可变。如山不可为水。水不可为山是也。至于虚空中逼塞者皆气也。而以其虚而无形也。故随时变化。或朝清明而暮阴曀。或朝阴曀而暮清明。变化无常矣。人之有心。亦虚明无形。故或自清而变为浊。或自浊而变为清矣。此其气质之可变者也。其机只在于志之一字。苟志于为舜。则一言之发。志于舜。一事之行。志于舜。一事二事。一年二年。以至于积久用力。则忽不自知其为舜矣。苟不志于为舜。则自一言一事背于舜。而终至于一生事事皆背于舜。则所以不能为舜也。此其众人之为舜与不为舜。只在于志之一字。伏愿于一志字上。深加意焉。 上曰。所论好矣。当留意焉。元震曰。臣之所 达心性名目之说。语涉支离。而必于心性名目有所见然后。工夫下手处。亦皆有著落。故敢以陈之矣。 上顾谓儒臣曰。予始欲儒臣录进经筵官心性之说矣。经筵官之意。似犹有未尽言者。使之录其所言。后日入侍时袖进可也。
但舜与众人。气质不同。而气质有可变之道。人之身体长短妍媸。固不可变也。至于心之虚明者。则可以变化矣。譬如天地之间。有形质者。皆不可变。如山不可为水。水不可为山是也。至于虚空中逼塞者皆气也。而以其虚而无形也。故随时变化。或朝清明而暮阴曀。或朝阴曀而暮清明。变化无常矣。人之有心。亦虚明无形。故或自清而变为浊。或自浊而变为清矣。此其气质之可变者也。其机只在于志之一字。苟志于为舜。则一言之发。志于舜。一事之行。志于舜。一事二事。一年二年。以至于积久用力。则忽不自知其为舜矣。苟不志于为舜。则自一言一事背于舜。而终至于一生事事皆背于舜。则所以不能为舜也。此其众人之为舜与不为舜。只在于志之一字。伏愿于一志字上。深加意焉。 上曰。所论好矣。当留意焉。元震曰。臣之所 达心性名目之说。语涉支离。而必于心性名目有所见然后。工夫下手处。亦皆有著落。故敢以陈之矣。 上顾谓儒臣曰。予始欲儒臣录进经筵官心性之说矣。经筵官之意。似犹有未尽言者。使之录其所言。后日入侍时袖进可也。九月初一日召对时。讲宋史高宗记下篇。元震曰。国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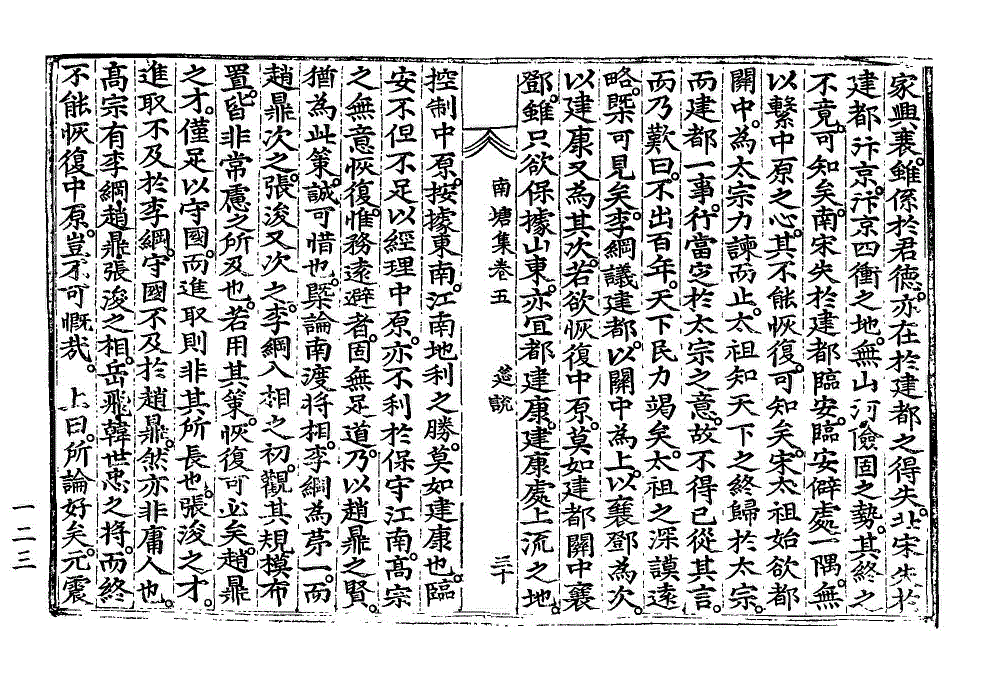 家兴衰。虽系于君德。亦在于建都之得失。北宋失于建都汴京。汴京四冲之地。无山河险固之势。其终之不竟。可知矣。南宋失于建都临安。临安僻处一隅。无以系中原之心。其不能恢复。可知矣。宋太祖始欲都关中。为太宗力谏而止。太祖知天下之终归于太宗。而建都一事。行当定于太宗之意。故不得已从其言。而乃叹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太祖之深谟远略。槩可见矣。李纲议建都。以关中为上。以襄邓为次。以建康又为其次。若欲恢复中原。莫如建都关中襄邓。虽只欲保据山东。亦宜都建康。建康处上流之地。控制中原。按据东南。江南地利之胜。莫如建康也。临安不但不足以经理中原。亦不利于保守江南。高宗之无意恢复。惟务远避者。固无足道。乃以赵鼎之贤。犹为此策。诚可惜也。槩论南渡将相。李纲为第一。而赵鼎次之。张浚又次之。李纲入相之初。观其规模布置。皆非常虑之所及也。若用其策。恢复可必矣。赵鼎之才。仅足以守国。而进取则非其所长也。张浚之才。进取不及于李纲。守国不及于赵鼎。然亦非庸人也。高宗有李纲,赵鼎,张浚之相。岳飞,韩世忠之将。而终不能恢复中原。岂不可慨哉。 上曰。所论好矣。元震
家兴衰。虽系于君德。亦在于建都之得失。北宋失于建都汴京。汴京四冲之地。无山河险固之势。其终之不竟。可知矣。南宋失于建都临安。临安僻处一隅。无以系中原之心。其不能恢复。可知矣。宋太祖始欲都关中。为太宗力谏而止。太祖知天下之终归于太宗。而建都一事。行当定于太宗之意。故不得已从其言。而乃叹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太祖之深谟远略。槩可见矣。李纲议建都。以关中为上。以襄邓为次。以建康又为其次。若欲恢复中原。莫如建都关中襄邓。虽只欲保据山东。亦宜都建康。建康处上流之地。控制中原。按据东南。江南地利之胜。莫如建康也。临安不但不足以经理中原。亦不利于保守江南。高宗之无意恢复。惟务远避者。固无足道。乃以赵鼎之贤。犹为此策。诚可惜也。槩论南渡将相。李纲为第一。而赵鼎次之。张浚又次之。李纲入相之初。观其规模布置。皆非常虑之所及也。若用其策。恢复可必矣。赵鼎之才。仅足以守国。而进取则非其所长也。张浚之才。进取不及于李纲。守国不及于赵鼎。然亦非庸人也。高宗有李纲,赵鼎,张浚之相。岳飞,韩世忠之将。而终不能恢复中原。岂不可慨哉。 上曰。所论好矣。元震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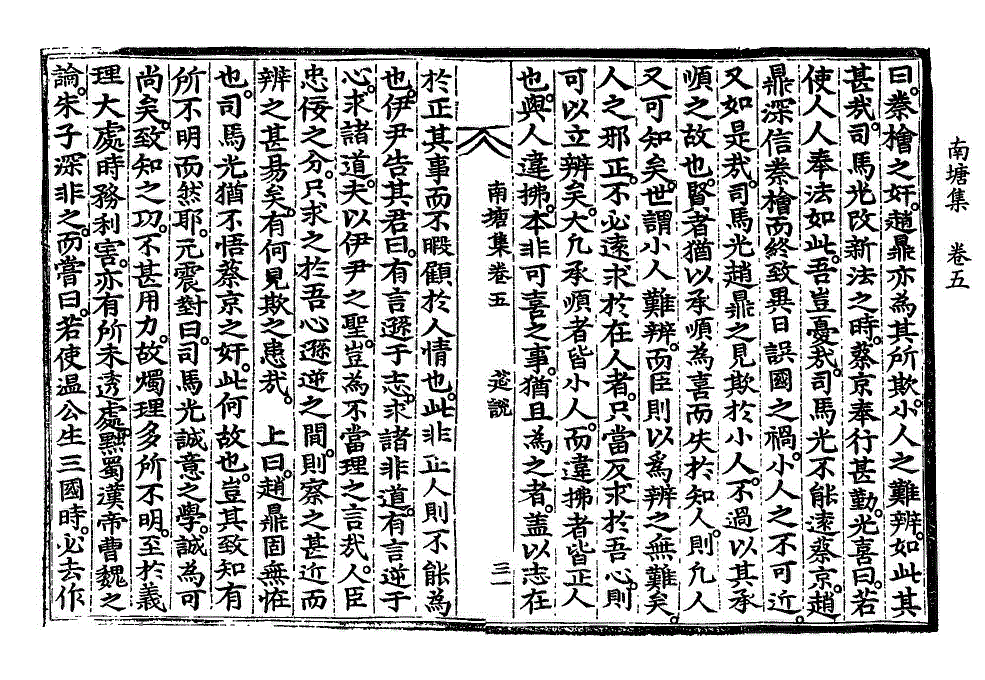 曰。秦桧之奸。赵鼎亦为其所欺。小人之难辨。如此其甚哉。司马光改新法之时。蔡京奉行甚勤。光喜曰。若使人人奉法如此。吾岂忧哉。司马光不能远蔡京。赵鼎深信秦桧而终致异日误国之祸。小人之不可近。又如是哉。司马光赵鼎之见欺于小人。不过以其承顺之故也。贤者犹以承顺为喜而失于知人。则凡人又可知矣。世谓小人难辨。而臣则以为辨之无难矣。人之邪正。不必远求于在人者。只当反求于吾心。则可以立辨矣。大凡承顺者皆小人。而违拂者皆正人也。与人违拂。本非可喜之事。犹且为之者。盖以志在于正其事而不暇顾于人情也。此非正人则不能为也。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逊于志。求诸非道。有言逆于心。求诸道。夫以伊尹之圣。岂为不当理之言哉。人臣忠佞之分。只求之于吾心逊逆之间。则察之甚近而辨之甚易矣。有何见欺之患哉。 上曰。赵鼎固无怪也。司马光犹不悟蔡京之奸。此何故也。岂其致知有所不明而然耶。元震对曰。司马光诚意之学。诚为可尚矣。致知之功。不甚用力。故烛理多所不明。至于义理大处时务利害。亦有所未透处。黜蜀汉帝曹魏之论。朱子深非之。而尝曰。若使温公生三国时。必去作
曰。秦桧之奸。赵鼎亦为其所欺。小人之难辨。如此其甚哉。司马光改新法之时。蔡京奉行甚勤。光喜曰。若使人人奉法如此。吾岂忧哉。司马光不能远蔡京。赵鼎深信秦桧而终致异日误国之祸。小人之不可近。又如是哉。司马光赵鼎之见欺于小人。不过以其承顺之故也。贤者犹以承顺为喜而失于知人。则凡人又可知矣。世谓小人难辨。而臣则以为辨之无难矣。人之邪正。不必远求于在人者。只当反求于吾心。则可以立辨矣。大凡承顺者皆小人。而违拂者皆正人也。与人违拂。本非可喜之事。犹且为之者。盖以志在于正其事而不暇顾于人情也。此非正人则不能为也。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逊于志。求诸非道。有言逆于心。求诸道。夫以伊尹之圣。岂为不当理之言哉。人臣忠佞之分。只求之于吾心逊逆之间。则察之甚近而辨之甚易矣。有何见欺之患哉。 上曰。赵鼎固无怪也。司马光犹不悟蔡京之奸。此何故也。岂其致知有所不明而然耶。元震对曰。司马光诚意之学。诚为可尚矣。致知之功。不甚用力。故烛理多所不明。至于义理大处时务利害。亦有所未透处。黜蜀汉帝曹魏之论。朱子深非之。而尝曰。若使温公生三国时。必去作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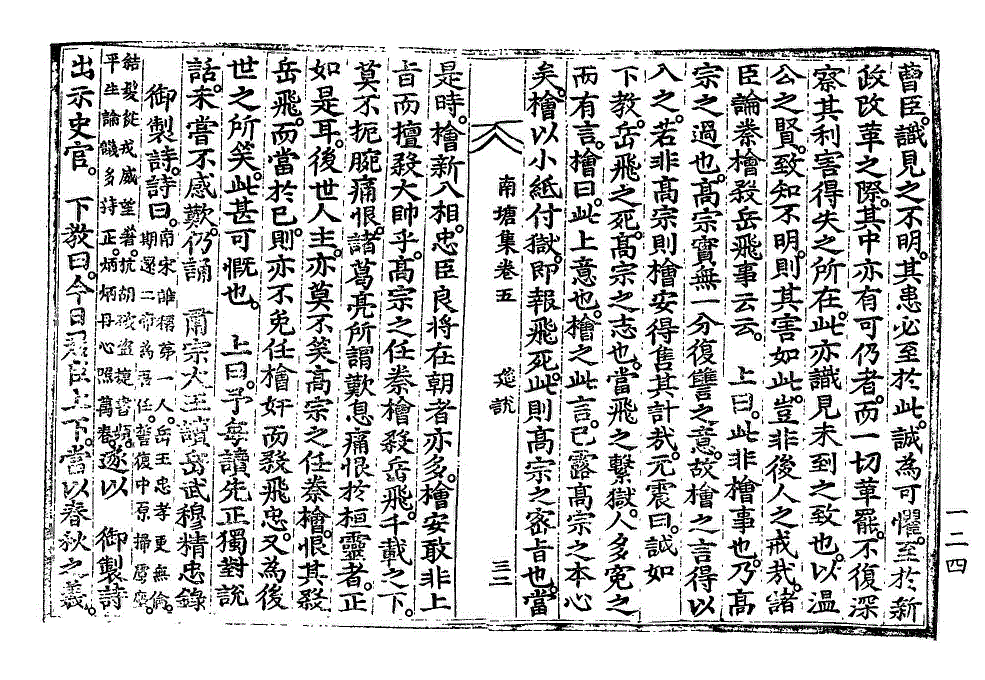 曹臣。识见之不明。其患必至于此。诚为可惧。至于新政改革之际。其中亦有可仍者。而一切革罢。不复深察其利害得失之所在。此亦识见未到之致也。以温公之贤。致知不明。则其害如此。岂非后人之戒哉。诸臣论秦桧杀岳飞事云云。 上曰。此非桧事也。乃高宗之过也。高宗实无一分复雠之意。故桧之言得以入之。若非高宗则桧安得售其计哉。元震曰。诚如 下教。岳飞之死。高宗之志也。当飞之系狱。人多冤之而有言。桧曰。此上意也。桧之此言。已露高宗之本心矣。桧以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此则高宗之密旨也。当是时。桧新入相。忠臣良将在朝者亦多。桧安敢非上旨而擅杀大帅乎。高宗之任秦桧杀岳飞。千载之下。莫不扼腕痛恨。诸葛亮所谓叹息痛恨于桓灵者。正如是耳。后世人主。亦莫不笑高宗之任秦桧。恨其杀岳飞。而当于己。则亦不免任桧奸而杀飞忠。又为后世之所笑。此甚可慨也。 上曰。予每读先正独对说话。未尝不感叹。仍诵 肃宗大王读岳武穆精忠录 御制诗。诗曰。(南宋谁称第一人。岳王忠孝更无伦。期还二帝为吾任。誓复中原扫虏尘。结发从戎威望著。抗胡破盗捷书频。平生论议多持正。炳炳丹心照万春。)遂以 御制诗出示史官。 下教曰。今日君臣上下。当以春秋之义。
曹臣。识见之不明。其患必至于此。诚为可惧。至于新政改革之际。其中亦有可仍者。而一切革罢。不复深察其利害得失之所在。此亦识见未到之致也。以温公之贤。致知不明。则其害如此。岂非后人之戒哉。诸臣论秦桧杀岳飞事云云。 上曰。此非桧事也。乃高宗之过也。高宗实无一分复雠之意。故桧之言得以入之。若非高宗则桧安得售其计哉。元震曰。诚如 下教。岳飞之死。高宗之志也。当飞之系狱。人多冤之而有言。桧曰。此上意也。桧之此言。已露高宗之本心矣。桧以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此则高宗之密旨也。当是时。桧新入相。忠臣良将在朝者亦多。桧安敢非上旨而擅杀大帅乎。高宗之任秦桧杀岳飞。千载之下。莫不扼腕痛恨。诸葛亮所谓叹息痛恨于桓灵者。正如是耳。后世人主。亦莫不笑高宗之任秦桧。恨其杀岳飞。而当于己。则亦不免任桧奸而杀飞忠。又为后世之所笑。此甚可慨也。 上曰。予每读先正独对说话。未尝不感叹。仍诵 肃宗大王读岳武穆精忠录 御制诗。诗曰。(南宋谁称第一人。岳王忠孝更无伦。期还二帝为吾任。誓复中原扫虏尘。结发从戎威望著。抗胡破盗捷书频。平生论议多持正。炳炳丹心照万春。)遂以 御制诗出示史官。 下教曰。今日君臣上下。当以春秋之义。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5H 页
 为第一务。予则当以 圣祖志事自期。群下则以先正之事自任可也。经筵官须毕陈其所蕴。元震进伏曰。 圣志卓然如此。实 宗社之幸也。然 殿下欲明春秋之义者。虽出于 诚心。而未见其见诸 行事。臣尝慨然。今承 圣教。使之毕陈所蕴。臣请仰达。目今生民之困日甚。境外之忧亦不小。今日廷臣虽不以此为忧。而人各思一计。亦岂无可救之策也。目前最急大事。犹未办得。故群情解体。无暇念及于他事。 殿下果知今日群下之心如此者乎。春秋之义。非但尊华攘夷也。诛乱臣讨贼子。以尊君父。最其大者也。 殿下欲明春秋之义。何不先自国中而为始乎。群下之所争。非为一己之私愤。实为国家讨贼也。 殿下之靳允。亦非有私意之系恋。臣知其出于好生之德也。今日大论。俱不系君臣上下一己之私事。而乃国家之大事。天下之公义也。君臣上下。正宜反覆讲确。务得其当。使之毋贻百世之讥而以示后王之法可也。伏愿 殿下平心听之。辛丑建 储代理之事。乃为 宗社建万世之策。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可以质鬼神而无疑。俟百世而不惑者也。于此而有异心者。岂非逆乎。凶党不但有异心。反指以为
为第一务。予则当以 圣祖志事自期。群下则以先正之事自任可也。经筵官须毕陈其所蕴。元震进伏曰。 圣志卓然如此。实 宗社之幸也。然 殿下欲明春秋之义者。虽出于 诚心。而未见其见诸 行事。臣尝慨然。今承 圣教。使之毕陈所蕴。臣请仰达。目今生民之困日甚。境外之忧亦不小。今日廷臣虽不以此为忧。而人各思一计。亦岂无可救之策也。目前最急大事。犹未办得。故群情解体。无暇念及于他事。 殿下果知今日群下之心如此者乎。春秋之义。非但尊华攘夷也。诛乱臣讨贼子。以尊君父。最其大者也。 殿下欲明春秋之义。何不先自国中而为始乎。群下之所争。非为一己之私愤。实为国家讨贼也。 殿下之靳允。亦非有私意之系恋。臣知其出于好生之德也。今日大论。俱不系君臣上下一己之私事。而乃国家之大事。天下之公义也。君臣上下。正宜反覆讲确。务得其当。使之毋贻百世之讥而以示后王之法可也。伏愿 殿下平心听之。辛丑建 储代理之事。乃为 宗社建万世之策。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可以质鬼神而无疑。俟百世而不惑者也。于此而有异心者。岂非逆乎。凶党不但有异心。反指以为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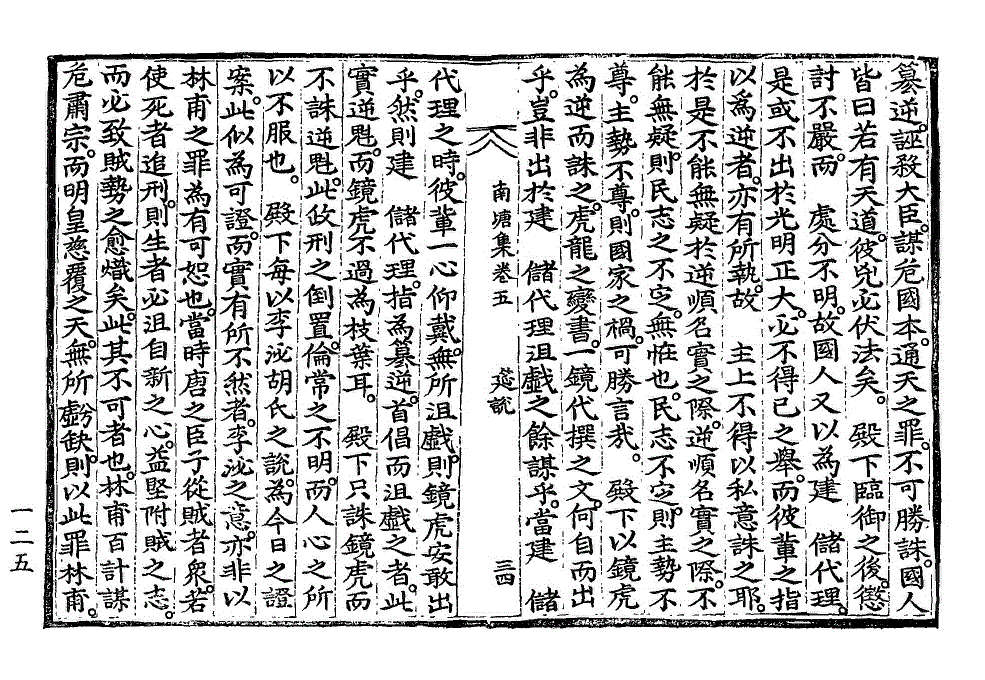 篡逆。诬杀大臣。谋危国本。通天之罪。不可胜诛。国人皆曰若有天道。彼凶必伏法矣。 殿下临御之后。惩讨不严。而 处分不明。故国人又以为建 储代理。是或不出于光明正大。必不得已之举。而彼辈之指以为逆者。亦有所执。故 主上不得以私意诛之耶。于是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逆顺名实之际。不能无疑。则民志之不定。无怪也。民志不定。则主势不尊。主势不尊。则国家之祸。可胜言哉。 殿下以镜虎为逆而诛之。虎龙之变书。一镜代撰之文。何自而出乎。岂非出于建 储代理沮戏之馀谋乎。当建 储代理之时。彼辈一心仰戴。无所沮戏。则镜虎安敢出乎。然则建 储代理。指为篡逆。首倡而沮戏之者。此实逆魁。而镜虎不过为枝叶耳。 殿下只诛镜虎而不诛逆魁。此政刑之倒置。伦常之不明。而人心之所以不服也。 殿下每以李泌胡氏之说。为今日之證案。此似为可證。而实有所不然者。李泌之意。亦非以林甫之罪为有可恕也。当时唐之臣子从贼者众。若使死者追刑。则生者必沮自新之心。益坚附贼之志。而必致贼势之愈炽矣。此其不可者也。林甫百计谋危肃宗。而明皇慈覆之天。无所亏缺。则以此罪林甫。
篡逆。诬杀大臣。谋危国本。通天之罪。不可胜诛。国人皆曰若有天道。彼凶必伏法矣。 殿下临御之后。惩讨不严。而 处分不明。故国人又以为建 储代理。是或不出于光明正大。必不得已之举。而彼辈之指以为逆者。亦有所执。故 主上不得以私意诛之耶。于是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逆顺名实之际。不能无疑。则民志之不定。无怪也。民志不定。则主势不尊。主势不尊。则国家之祸。可胜言哉。 殿下以镜虎为逆而诛之。虎龙之变书。一镜代撰之文。何自而出乎。岂非出于建 储代理沮戏之馀谋乎。当建 储代理之时。彼辈一心仰戴。无所沮戏。则镜虎安敢出乎。然则建 储代理。指为篡逆。首倡而沮戏之者。此实逆魁。而镜虎不过为枝叶耳。 殿下只诛镜虎而不诛逆魁。此政刑之倒置。伦常之不明。而人心之所以不服也。 殿下每以李泌胡氏之说。为今日之證案。此似为可證。而实有所不然者。李泌之意。亦非以林甫之罪为有可恕也。当时唐之臣子从贼者众。若使死者追刑。则生者必沮自新之心。益坚附贼之志。而必致贼势之愈炽矣。此其不可者也。林甫百计谋危肃宗。而明皇慈覆之天。无所亏缺。则以此罪林甫。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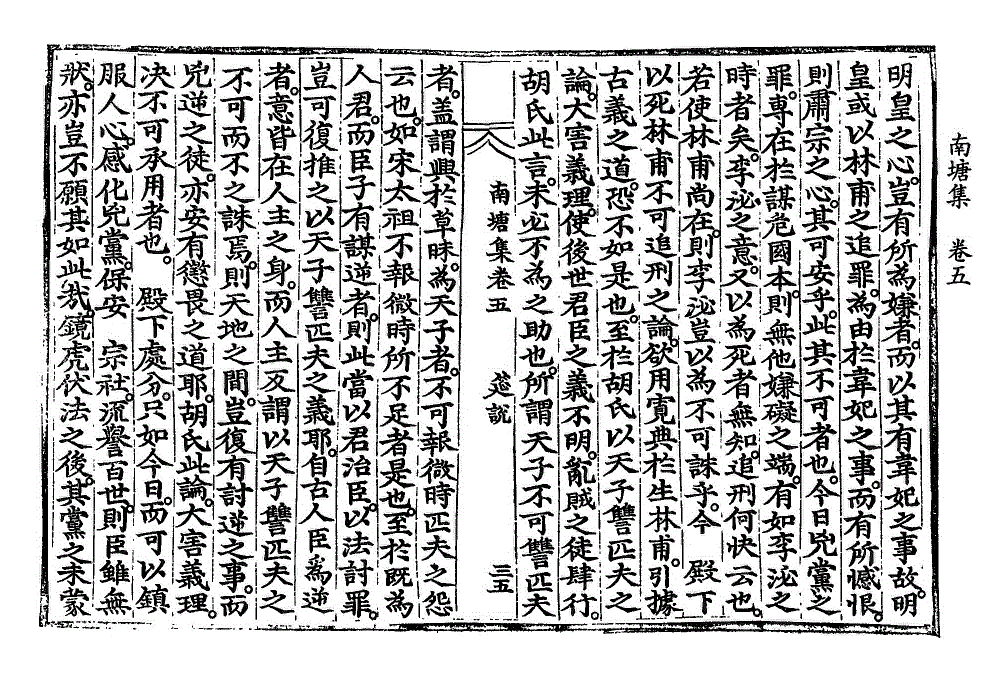 明皇之心。岂有所为嫌者。而以其有韦妃之事故。明皇或以林甫之追罪。为由于韦妃之事。而有所憾恨。则肃宗之心。其可安乎。此其不可者也。今日凶党之罪。专在于谋危国本。则无他嫌碍之端。有如李泌之时者矣。李泌之意。又以为死者无知。追刑何快云也。若使林甫尚在。则李泌岂以为不可诛乎。今 殿下以死林甫不可追刑之论。欲用宽典于生林甫。引据古义之道。恐不如是也。至于胡氏以天子雠匹夫之论。大害义理。使后世君臣之义不明。乱贼之徒肆行。胡氏此言。未必不为之助也。所谓天子不可雠匹夫者。盖谓兴于草昧。为天子者。不可报微时匹夫之怨云也。如宋太祖不报微时所不足者是也。至于既为人君。而臣子有谋逆者。则此当以君治臣。以法讨罪。岂可复推之以天子雠匹夫之义耶。自古人臣为逆者。意皆在人主之身。而人主反谓以天子雠匹夫之不可而不之诛焉。则天地之间。岂复有讨逆之事。而凶逆之徒。亦安有惩畏之道耶。胡氏此论。大害义理。决不可承用者也。 殿下处分。只如今日。而可以镇服人心。感化凶党。保安 宗社。流誉百世。则臣虽无状。亦岂不愿其如此哉。镜虎伏法之后。其党之未蒙
明皇之心。岂有所为嫌者。而以其有韦妃之事故。明皇或以林甫之追罪。为由于韦妃之事。而有所憾恨。则肃宗之心。其可安乎。此其不可者也。今日凶党之罪。专在于谋危国本。则无他嫌碍之端。有如李泌之时者矣。李泌之意。又以为死者无知。追刑何快云也。若使林甫尚在。则李泌岂以为不可诛乎。今 殿下以死林甫不可追刑之论。欲用宽典于生林甫。引据古义之道。恐不如是也。至于胡氏以天子雠匹夫之论。大害义理。使后世君臣之义不明。乱贼之徒肆行。胡氏此言。未必不为之助也。所谓天子不可雠匹夫者。盖谓兴于草昧。为天子者。不可报微时匹夫之怨云也。如宋太祖不报微时所不足者是也。至于既为人君。而臣子有谋逆者。则此当以君治臣。以法讨罪。岂可复推之以天子雠匹夫之义耶。自古人臣为逆者。意皆在人主之身。而人主反谓以天子雠匹夫之不可而不之诛焉。则天地之间。岂复有讨逆之事。而凶逆之徒。亦安有惩畏之道耶。胡氏此论。大害义理。决不可承用者也。 殿下处分。只如今日。而可以镇服人心。感化凶党。保安 宗社。流誉百世。则臣虽无状。亦岂不愿其如此哉。镜虎伏法之后。其党之未蒙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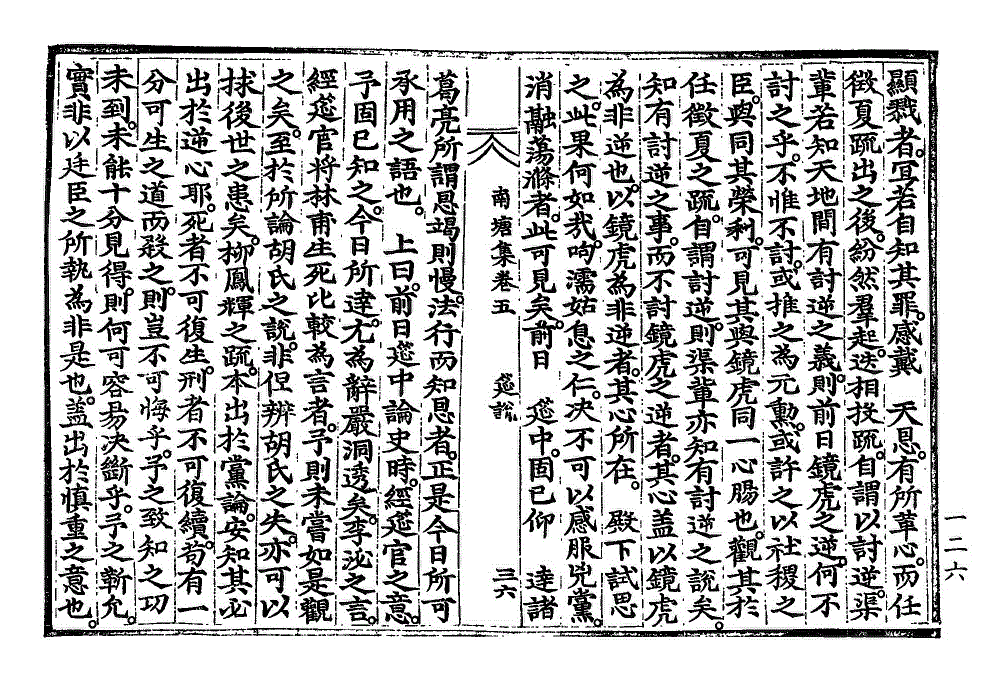 显戮者。宜若自知其罪。感戴 天恩。有所革心。而任徵夏疏出之后。纷然群起。迭相投疏。自谓以讨逆。渠辈若知天地间有讨逆之义。则前日镜虎之逆。何不讨之乎。不惟不讨。或推之为元勋。或许之以社稷之臣。与同其荣利。可见其与镜虎同一心肠也。观其于任徵夏之疏。自谓讨逆。则渠辈亦知有讨逆之说矣。知有讨逆之事。而不讨镜虎之逆者。其心盖以镜虎为非逆也。以镜虎为非逆者。其心所在。 殿下试思之。此果何如哉。呴濡姑息之仁。决不可以感服凶党。消融荡涤者。此可见矣。前日 筵中。固已仰 达诸葛亮所谓恩竭则慢。法行而知恩者。正是今日所可承用之语也。 上曰。前日筵中论史时。经筵官之意。予固已知之。今日所达。尤为辞严洞透矣。李泌之言。经筵官将林甫生死比较为言者。予则未尝如是观之矣。至于所论胡氏之说。非但辨胡氏之失。亦可以救后世之患矣。柳凤辉之疏。本出于党论。安知其必出于逆心耶。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苟有一分可生之道而杀之。则岂不可悔乎。予之致知之功未到。未能十分见得。则何可容易决断乎。予之靳允。实非以廷臣之所执为非是也。盖出于慎重之意也。
显戮者。宜若自知其罪。感戴 天恩。有所革心。而任徵夏疏出之后。纷然群起。迭相投疏。自谓以讨逆。渠辈若知天地间有讨逆之义。则前日镜虎之逆。何不讨之乎。不惟不讨。或推之为元勋。或许之以社稷之臣。与同其荣利。可见其与镜虎同一心肠也。观其于任徵夏之疏。自谓讨逆。则渠辈亦知有讨逆之说矣。知有讨逆之事。而不讨镜虎之逆者。其心盖以镜虎为非逆也。以镜虎为非逆者。其心所在。 殿下试思之。此果何如哉。呴濡姑息之仁。决不可以感服凶党。消融荡涤者。此可见矣。前日 筵中。固已仰 达诸葛亮所谓恩竭则慢。法行而知恩者。正是今日所可承用之语也。 上曰。前日筵中论史时。经筵官之意。予固已知之。今日所达。尤为辞严洞透矣。李泌之言。经筵官将林甫生死比较为言者。予则未尝如是观之矣。至于所论胡氏之说。非但辨胡氏之失。亦可以救后世之患矣。柳凤辉之疏。本出于党论。安知其必出于逆心耶。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苟有一分可生之道而杀之。则岂不可悔乎。予之致知之功未到。未能十分见得。则何可容易决断乎。予之靳允。实非以廷臣之所执为非是也。盖出于慎重之意也。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7H 页
 元震曰。杀人者死。三尺至严。朱子曰。人命至重。官司何以斩之于市。只为佗曾杀那人。故不杀佗。那人之怨不解。凶党诬起大狱。屠戮忠贤。只此为罪。已可以诛之。况其所以屠戮者。本出于为逆。则其罪又岂可胜诛乎。凤辉之事。推其本源。固出于党论。而至今所犯。既在于逆。则当以逆治之。岂可推恕以党论乎。程子言四凶见大舜之受禅。有愤惋不平之意。故大舜诛之。四凶之于大舜。只有愤惋不平之意而已。未见其有沮戏传授之事者。而大舜犹诛之。三叔之称乱。本出于媢嫉周公之摄政。而周公犹致辟焉。大舜,周公只讨其逆。而未尝有原情之事。今于凤辉。何可曲为原情之论乎。 上曰。三代以后用刑。与三代以上。似当有异矣。元震曰。臣又有所仰 达者。申致云之诬辱臣师。亦世道之一大变怪也。臣师之道德行谊。臣不暇论。而第臣师生而为 圣考之所尊礼。殁而为竖子之所戮辱。恶名狼藉。九原含痛。使当日凶党若有一分尊畏 圣考之心。则岂有此事哉。 殿下于臣师。复官赐谥。遣官致祭。 许令建院。则臣师冤枉。亦可谓昭雪。而虽是薄罚。亦罪致云。则是非亦可谓定矣。然致云之罚。不当其罪。则臣师之诬。未可谓
元震曰。杀人者死。三尺至严。朱子曰。人命至重。官司何以斩之于市。只为佗曾杀那人。故不杀佗。那人之怨不解。凶党诬起大狱。屠戮忠贤。只此为罪。已可以诛之。况其所以屠戮者。本出于为逆。则其罪又岂可胜诛乎。凤辉之事。推其本源。固出于党论。而至今所犯。既在于逆。则当以逆治之。岂可推恕以党论乎。程子言四凶见大舜之受禅。有愤惋不平之意。故大舜诛之。四凶之于大舜。只有愤惋不平之意而已。未见其有沮戏传授之事者。而大舜犹诛之。三叔之称乱。本出于媢嫉周公之摄政。而周公犹致辟焉。大舜,周公只讨其逆。而未尝有原情之事。今于凤辉。何可曲为原情之论乎。 上曰。三代以后用刑。与三代以上。似当有异矣。元震曰。臣又有所仰 达者。申致云之诬辱臣师。亦世道之一大变怪也。臣师之道德行谊。臣不暇论。而第臣师生而为 圣考之所尊礼。殁而为竖子之所戮辱。恶名狼藉。九原含痛。使当日凶党若有一分尊畏 圣考之心。则岂有此事哉。 殿下于臣师。复官赐谥。遣官致祭。 许令建院。则臣师冤枉。亦可谓昭雪。而虽是薄罚。亦罪致云。则是非亦可谓定矣。然致云之罚。不当其罪。则臣师之诬。未可谓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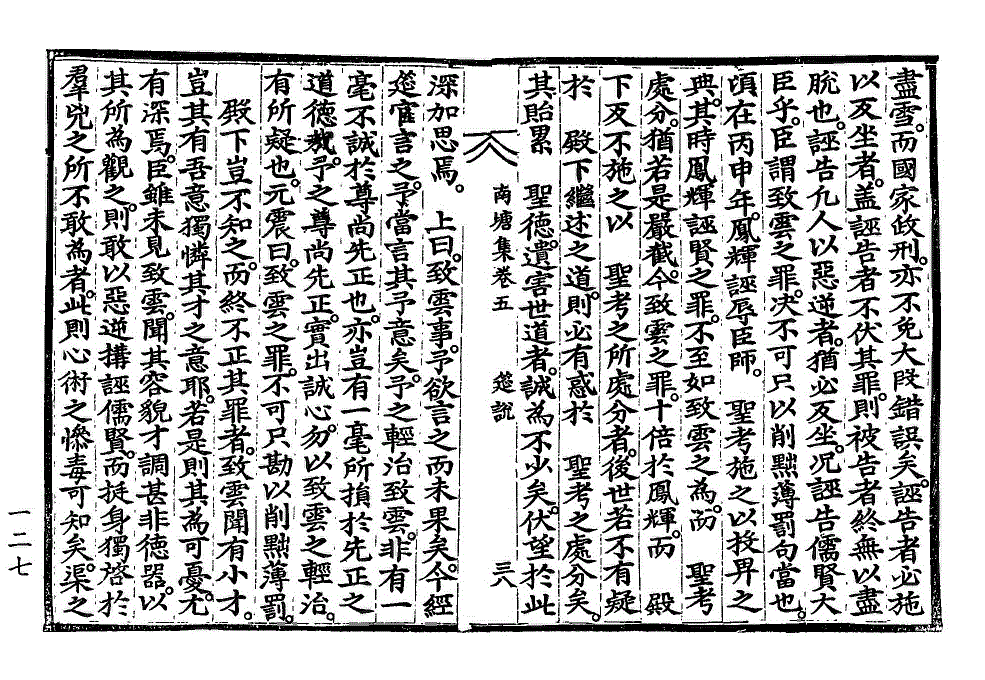 尽雪。而国家政刑。亦不免大段错误矣。诬告者必施以反坐者。盖诬告者不伏其罪。则被告者终无以尽脱也。诬告凡人以恶逆者。犹必反坐。况诬告儒贤大臣乎。臣谓致云之罪。决不可只以削黜薄罚句当也。顷在丙申年。凤辉诬辱臣师。 圣考施之以投畀之典。其时凤辉诬贤之罪。不至如致云之为。而 圣考处分。犹若是严截。今致云之罪。十倍于凤辉。而 殿下反不施之以 圣考之所处分者。后世若不有疑于 殿下继述之道。则必有惑于 圣考之处分矣。其贻累 圣德。遗害世道者。诚为不少矣。伏望于此深加思焉。 上曰。致云事。予欲言之而未果矣。今经筵官言之。予当言其予意矣。予之轻治致云。非有一毫不诚于尊尚先正也。亦岂有一毫所损于先正之道德哉。予之尊尚先正。实出诚心。勿以致云之轻治。有所疑也。元震曰。致云之罪。不可只勘以削黜薄罚。 殿下岂不知之。而终不正其罪者。致云闻有小才。岂其有吾意独怜其才之意耶。若是则其为可忧。尤有深焉。臣虽未见致云。闻其容貌才调甚非德器。以其所为观之。则敢以恶逆搆诬儒贤。而挺身独启于群凶之所不敢为者。此则心术之惨毒可知矣。渠之
尽雪。而国家政刑。亦不免大段错误矣。诬告者必施以反坐者。盖诬告者不伏其罪。则被告者终无以尽脱也。诬告凡人以恶逆者。犹必反坐。况诬告儒贤大臣乎。臣谓致云之罪。决不可只以削黜薄罚句当也。顷在丙申年。凤辉诬辱臣师。 圣考施之以投畀之典。其时凤辉诬贤之罪。不至如致云之为。而 圣考处分。犹若是严截。今致云之罪。十倍于凤辉。而 殿下反不施之以 圣考之所处分者。后世若不有疑于 殿下继述之道。则必有惑于 圣考之处分矣。其贻累 圣德。遗害世道者。诚为不少矣。伏望于此深加思焉。 上曰。致云事。予欲言之而未果矣。今经筵官言之。予当言其予意矣。予之轻治致云。非有一毫不诚于尊尚先正也。亦岂有一毫所损于先正之道德哉。予之尊尚先正。实出诚心。勿以致云之轻治。有所疑也。元震曰。致云之罪。不可只勘以削黜薄罚。 殿下岂不知之。而终不正其罪者。致云闻有小才。岂其有吾意独怜其才之意耶。若是则其为可忧。尤有深焉。臣虽未见致云。闻其容貌才调甚非德器。以其所为观之。则敢以恶逆搆诬儒贤。而挺身独启于群凶之所不敢为者。此则心术之惨毒可知矣。渠之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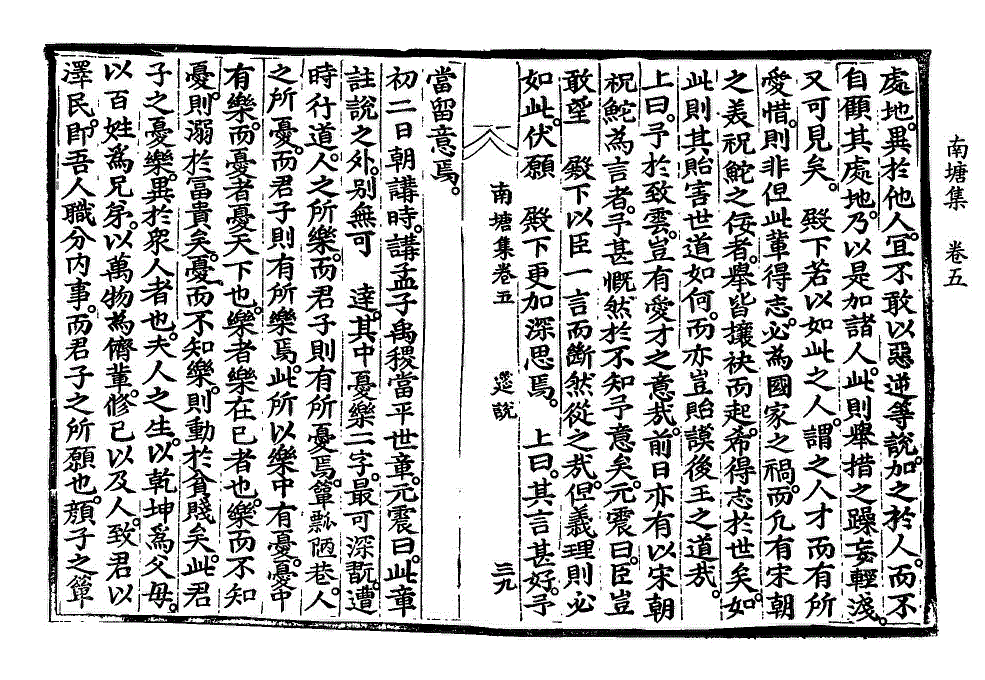 处地。异于他人。宜不敢以恶逆等说。加之于人。而不自顾其处地。乃以是加诸人。此则举措之躁妄轻浅。又可见矣。 殿下若以如此之人。谓之人才而有所爱惜。则非但此辈得志。必为国家之祸。而凡有宋朝之美祝鮀之佞者。举皆攘袂而起。希得志于世矣。如此则其贻害世道如何。而亦岂贻谟后王之道哉。 上曰。予于致云。岂有爱才之意哉。前日亦有以宋朝祝鮀为言者。予甚慨然于不知予意矣。元震曰。臣岂敢望 殿下以臣一言而断然从之哉。但义理则必如此。伏愿 殿下更加深思焉。 上曰。其言甚好。予当留意焉。
处地。异于他人。宜不敢以恶逆等说。加之于人。而不自顾其处地。乃以是加诸人。此则举措之躁妄轻浅。又可见矣。 殿下若以如此之人。谓之人才而有所爱惜。则非但此辈得志。必为国家之祸。而凡有宋朝之美祝鮀之佞者。举皆攘袂而起。希得志于世矣。如此则其贻害世道如何。而亦岂贻谟后王之道哉。 上曰。予于致云。岂有爱才之意哉。前日亦有以宋朝祝鮀为言者。予甚慨然于不知予意矣。元震曰。臣岂敢望 殿下以臣一言而断然从之哉。但义理则必如此。伏愿 殿下更加深思焉。 上曰。其言甚好。予当留意焉。初二日朝讲时。讲孟子禹稷当平世章。元震曰。此章注说之外。别无可 达。其中忧乐二字。最可深玩。遭时行道。人之所乐。而君子则有所忧焉。箪瓢陋巷。人之所忧。而君子则有所乐焉。此所以乐中有忧。忧中有乐。而忧者忧天下也。乐者乐在己者也。乐而不知忧。则溺于富贵矣。忧而不知乐。则动于贫贱矣。此君子之忧乐。异于众人者也。夫人之生。以乾坤为父母。以百姓为兄弟。以万物为侪辈。修己以及人。致君以泽民。即吾人职分内事。而君子之所愿也。颜子之箪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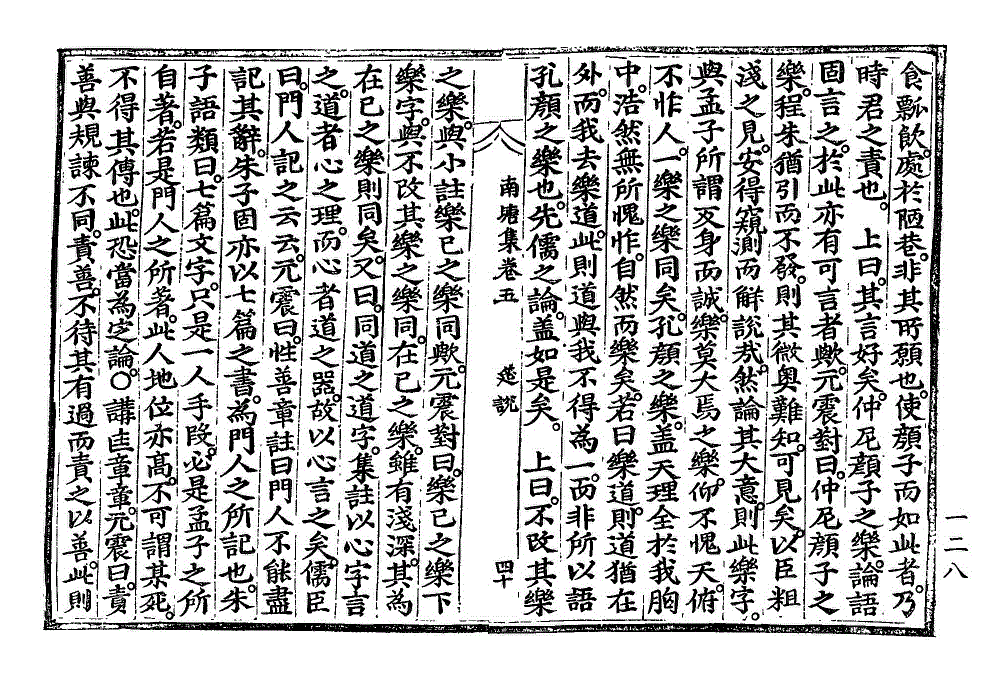 食瓢饮。处于陋巷。非其所愿也。使颜子而如此者。乃时君之责也。 上曰。其言好矣。仲尼颜子之乐。论语固言之。于此亦有可言者欤。元震对曰。仲尼颜子之乐。程朱犹引而不发。则其微奥难知。可见矣。以臣粗浅之见。安得窥测而解说哉。然论其大意。则此乐字。与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乐。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一乐之乐同矣。孔颜之乐。盖天理全于我胸中。浩然无所愧怍。自然而乐矣。若曰乐道。则道犹在外。而我去乐道。此则道与我不得为一。而非所以语孔颜之乐也。先儒之论。盖如是矣。 上曰。不改其乐之乐。与小注乐己之乐同欤。元震对曰。乐己之乐下乐字。与不改其乐之乐同。在己之乐。虽有浅深。其为在己之乐则同矣。又曰。同道之道字。集注以心字言之。道者心之理。而心者道之器。故以心言之矣。儒臣曰。门人记之云云。元震曰。性善章注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辞。朱子固亦以七篇之书。为门人之所记也。朱子语类曰。七篇文字。只是一人手段。必是孟子之所自著。若是门人之所著。此人地位亦高。不可谓某死。不得其传也。此恐当为定论。○讲匡章章。元震曰。责善与规谏不同。责善。不待其有过而责之以善。此则
食瓢饮。处于陋巷。非其所愿也。使颜子而如此者。乃时君之责也。 上曰。其言好矣。仲尼颜子之乐。论语固言之。于此亦有可言者欤。元震对曰。仲尼颜子之乐。程朱犹引而不发。则其微奥难知。可见矣。以臣粗浅之见。安得窥测而解说哉。然论其大意。则此乐字。与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乐。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一乐之乐同矣。孔颜之乐。盖天理全于我胸中。浩然无所愧怍。自然而乐矣。若曰乐道。则道犹在外。而我去乐道。此则道与我不得为一。而非所以语孔颜之乐也。先儒之论。盖如是矣。 上曰。不改其乐之乐。与小注乐己之乐同欤。元震对曰。乐己之乐下乐字。与不改其乐之乐同。在己之乐。虽有浅深。其为在己之乐则同矣。又曰。同道之道字。集注以心字言之。道者心之理。而心者道之器。故以心言之矣。儒臣曰。门人记之云云。元震曰。性善章注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辞。朱子固亦以七篇之书。为门人之所记也。朱子语类曰。七篇文字。只是一人手段。必是孟子之所自著。若是门人之所著。此人地位亦高。不可谓某死。不得其传也。此恐当为定论。○讲匡章章。元震曰。责善与规谏不同。责善。不待其有过而责之以善。此则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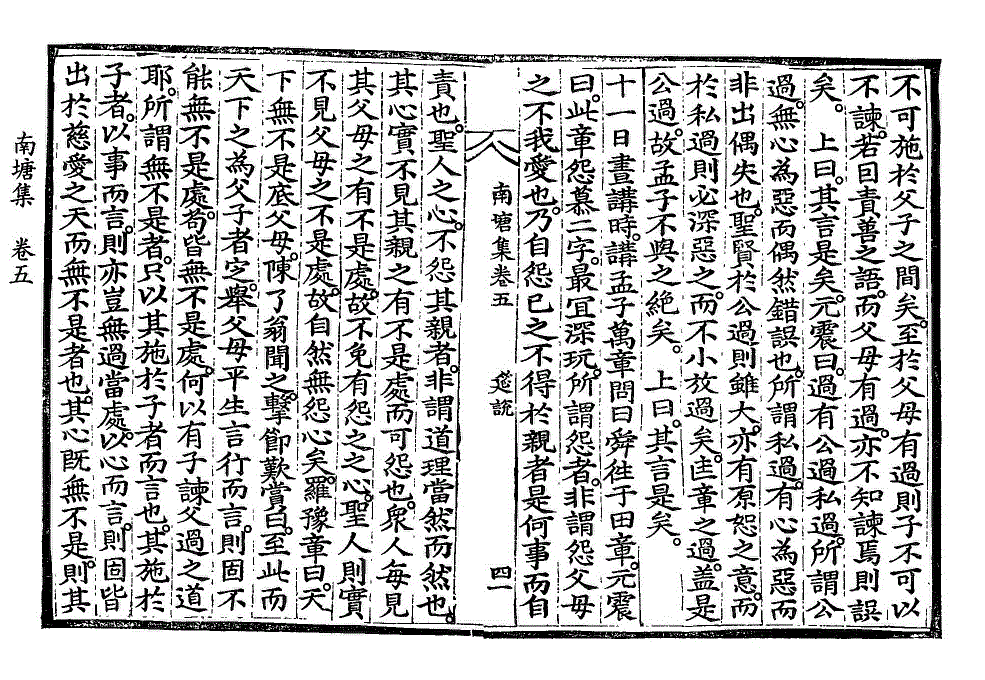 不可施于父子之间矣。至于父母有过则子不可以不谏。若因责善之语。而父母有过。亦不知谏焉则误矣。 上曰。其言是矣。元震曰。过有公过私过。所谓公过。无心为恶而偶然错误也。所谓私过。有心为恶而非出偶失也。圣贤于公过则虽大。亦有原恕之意。而于私过则必深恶之。而不小放过矣。匡章之过。盖是公过。故孟子不与之绝矣。 上曰。其言是矣。
不可施于父子之间矣。至于父母有过则子不可以不谏。若因责善之语。而父母有过。亦不知谏焉则误矣。 上曰。其言是矣。元震曰。过有公过私过。所谓公过。无心为恶而偶然错误也。所谓私过。有心为恶而非出偶失也。圣贤于公过则虽大。亦有原恕之意。而于私过则必深恶之。而不小放过矣。匡章之过。盖是公过。故孟子不与之绝矣。 上曰。其言是矣。十一日昼讲时。讲孟子万章问曰舜往于田章。元震曰。此章怨慕二字。最宜深玩。所谓怨者。非谓怨父母之不我爱也。乃自怨己之不得于亲者是何事而自责也。圣人之心。不怨其亲者。非谓道理当然而然也。其心实不见其亲之有不是处而可怨也。众人每见其父母之有不是处。故不免有怨之之心。圣人则实不见父母之不是处。故自然无怨心矣。罗豫章曰。天下无不是底父母。陈了翁闻之。击节叹赏曰。至此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举父母平生言行而言。则固不能无不是处。苟皆无不是处。何以有子谏父过之道耶。所谓无不是者。只以其施于子者而言也。其施于子者。以事而言。则亦岂无过当处。以心而言。则固皆出于慈爱之天而无不是者也。其心既无不是。则其
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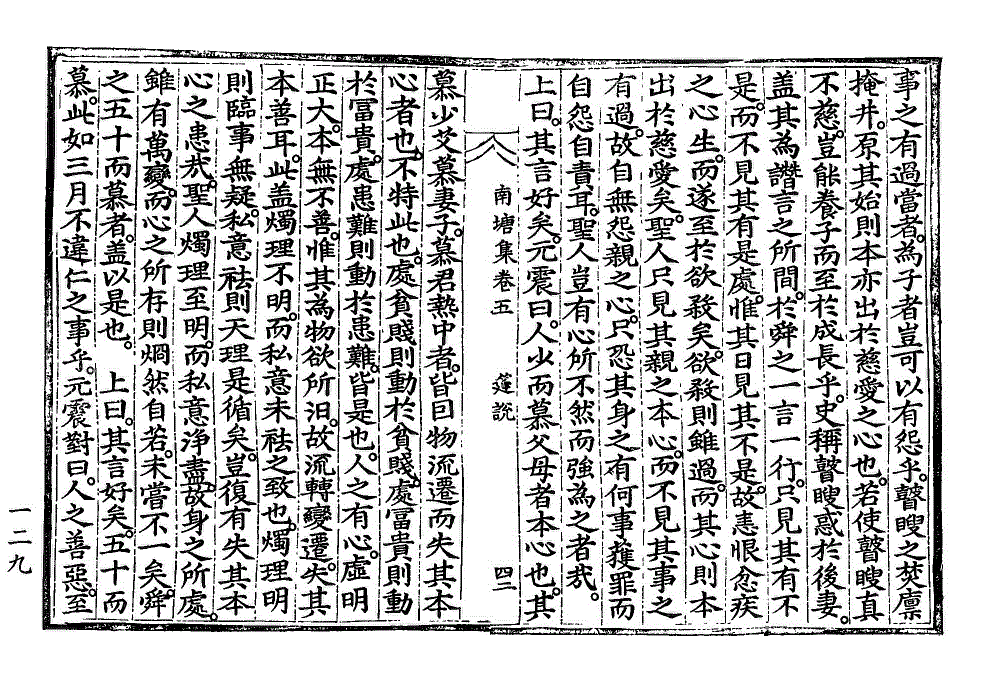 事之有过当者。为子者岂可以有怨乎。瞽瞍之焚廪掩井。原其始则本亦出于慈爱之心也。若使瞽瞍真不慈。岂能养子而至于成长乎。史称瞽瞍惑于后妻。盖其为谮言之所间。于舜之一言一行。只见其有不是。而不见其有是处。惟其日见其不是。故恚恨忿疾之心生。而遂至于欲杀矣。欲杀则虽过。而其心则本出于慈爱矣。圣人只见其亲之本心。而不见其事之有过。故自无怨亲之心。只恐其身之有何事获罪而自怨自责耳。圣人岂有心所不然而强为之者哉。 上曰。其言好矣。元震曰。人少而慕父母者本心也。其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热中者。皆因物流迁而失其本心者也。不特此也。处贫贱则动于贫贱。处富贵则动于富贵。处患难则动于患难。皆是也。人之有心。虚明正大。本无不善。惟其为物欲所汨。故流转变迁。失其本善耳。此盖烛理不明。而私意未祛之致也。烛理明则临事无疑。私意祛则天理是循矣。岂复有失其本心之患哉。圣人烛理至明。而私意净尽。故身之所处。虽有万变。而心之所存则烱然自若。未尝不一矣。舜之五十而慕者。盖以是也。 上曰。其言好矣。五十而慕。此如三月不违仁之事乎。元震对曰。人之善恶。至
事之有过当者。为子者岂可以有怨乎。瞽瞍之焚廪掩井。原其始则本亦出于慈爱之心也。若使瞽瞍真不慈。岂能养子而至于成长乎。史称瞽瞍惑于后妻。盖其为谮言之所间。于舜之一言一行。只见其有不是。而不见其有是处。惟其日见其不是。故恚恨忿疾之心生。而遂至于欲杀矣。欲杀则虽过。而其心则本出于慈爱矣。圣人只见其亲之本心。而不见其事之有过。故自无怨亲之心。只恐其身之有何事获罪而自怨自责耳。圣人岂有心所不然而强为之者哉。 上曰。其言好矣。元震曰。人少而慕父母者本心也。其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热中者。皆因物流迁而失其本心者也。不特此也。处贫贱则动于贫贱。处富贵则动于富贵。处患难则动于患难。皆是也。人之有心。虚明正大。本无不善。惟其为物欲所汨。故流转变迁。失其本善耳。此盖烛理不明。而私意未祛之致也。烛理明则临事无疑。私意祛则天理是循矣。岂复有失其本心之患哉。圣人烛理至明。而私意净尽。故身之所处。虽有万变。而心之所存则烱然自若。未尝不一矣。舜之五十而慕者。盖以是也。 上曰。其言好矣。五十而慕。此如三月不违仁之事乎。元震对曰。人之善恶。至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0H 页
 于四十五十而皆定。不可复变矣。孔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亦不足畏也。此以不善定也。舜五十而慕者。以善定也。五十而慕。则终身而慕者。在其中矣。至于三月不违仁者。三月之后。未免有违仁之时矣。此颜子之所以去圣人一间者也。然三月天时少变之节。而能不违仁于其间。则其心之纯乎天理者久矣。而其所谓违仁者。亦只是一念之少差。才差失。便能觉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又颜子之几于圣。而假之以年。不日而化者矣。此三月不违仁。与五十而慕者。所指不同矣。 上曰。予于三月不违仁之意。今方晓然矣。孟子称曾子之孝曰可也。可也者。仅可之辞也。若使曾子处大舜之地。亦能如大舜之所以处之者乎。元震对曰。曾晰之为人。性甚严急。其施于子者。亦多有过当处。曾子之所以事之者。一皆承顺而无怨怼不恭之心。则虽使处大舜之地。其所处之者。亦必如大舜矣。但曾子则不免用力为之。而大舜则自然而然。无所勉强矣。大舜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曾子思而后得。勉而后中者也。大舜曾子处事必无不同。而其所以处之者。有安行利行之不同耳。此则圣贤之所以分也。 上曰。其言好矣。○讲万章问曰诗云娶妻
于四十五十而皆定。不可复变矣。孔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亦不足畏也。此以不善定也。舜五十而慕者。以善定也。五十而慕。则终身而慕者。在其中矣。至于三月不违仁者。三月之后。未免有违仁之时矣。此颜子之所以去圣人一间者也。然三月天时少变之节。而能不违仁于其间。则其心之纯乎天理者久矣。而其所谓违仁者。亦只是一念之少差。才差失。便能觉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又颜子之几于圣。而假之以年。不日而化者矣。此三月不违仁。与五十而慕者。所指不同矣。 上曰。予于三月不违仁之意。今方晓然矣。孟子称曾子之孝曰可也。可也者。仅可之辞也。若使曾子处大舜之地。亦能如大舜之所以处之者乎。元震对曰。曾晰之为人。性甚严急。其施于子者。亦多有过当处。曾子之所以事之者。一皆承顺而无怨怼不恭之心。则虽使处大舜之地。其所处之者。亦必如大舜矣。但曾子则不免用力为之。而大舜则自然而然。无所勉强矣。大舜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曾子思而后得。勉而后中者也。大舜曾子处事必无不同。而其所以处之者。有安行利行之不同耳。此则圣贤之所以分也。 上曰。其言好矣。○讲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0L 页
 如之何章。元震曰。此章忧喜二字。最宜深玩。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自常人观之。则其所忧喜。似若有伪。其诚信而忧喜。亦似甚迂。然以弟思兄而来见。是人情天理之所当然者也。彼之来既出于人情天理之所当然。则圣人安得不诚信也。既已诚信。则自不得不忧其忧喜其喜矣。圣人不迂。亦无伪矣。若于人情天理之所当然处。逆探其恶。不为诚信。则在我亦不免人情天理之有未至者矣。圣人岂如是哉。前章怨慕。实见得父母之无不是处而自无怨心。此章忧喜。亦只见得兄弟相爱之心而诚信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只在于此。而圣凡之所以分。亦只在于诚伪之间而已矣。 上曰。其言好矣。元震曰。舜之称以大孝。始著于中庸。中庸之称大孝。不举善事父母之事。而乃以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称之。如此然后。方可为孝之大也。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固非人人之所可言。承宗祀庇子孙。匹庶亦所当勉。尊为天子以下推其本。则在于德为圣人。德为圣人。亦有其道。中庸称大舜曰。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孟子称大舜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为善。舜之聪明圣智。所可称者何限。而
如之何章。元震曰。此章忧喜二字。最宜深玩。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自常人观之。则其所忧喜。似若有伪。其诚信而忧喜。亦似甚迂。然以弟思兄而来见。是人情天理之所当然者也。彼之来既出于人情天理之所当然。则圣人安得不诚信也。既已诚信。则自不得不忧其忧喜其喜矣。圣人不迂。亦无伪矣。若于人情天理之所当然处。逆探其恶。不为诚信。则在我亦不免人情天理之有未至者矣。圣人岂如是哉。前章怨慕。实见得父母之无不是处而自无怨心。此章忧喜。亦只见得兄弟相爱之心而诚信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只在于此。而圣凡之所以分。亦只在于诚伪之间而已矣。 上曰。其言好矣。元震曰。舜之称以大孝。始著于中庸。中庸之称大孝。不举善事父母之事。而乃以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称之。如此然后。方可为孝之大也。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固非人人之所可言。承宗祀庇子孙。匹庶亦所当勉。尊为天子以下推其本。则在于德为圣人。德为圣人。亦有其道。中庸称大舜曰。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孟子称大舜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为善。舜之聪明圣智。所可称者何限。而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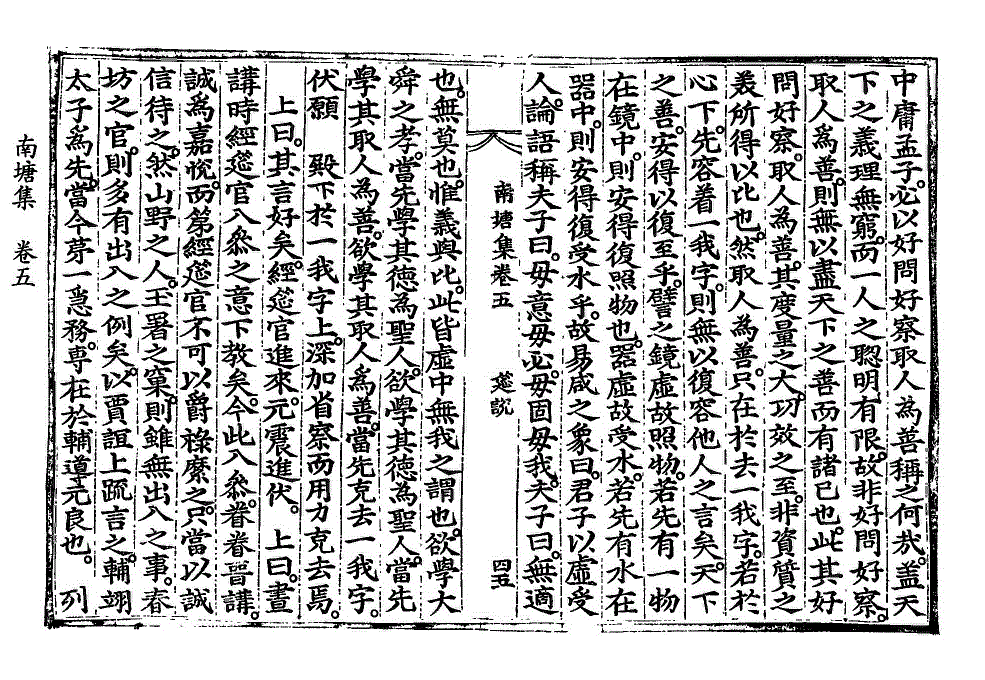 中庸孟子。必以好问好察取人为善称之何哉。盖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一人之聪明有限。故非好问好察。取人为善。则无以尽天下之善而有诸己也。此其好问好察。取人为善。其度量之大。功效之至。非资质之美所得以比也。然取人为善。只在于去一我字。若于心下。先容着一我字。则无以复容他人之言矣。天下之善。安得以复至乎。譬之镜虚故照物。若先有一物在镜中。则安得复照物也。器虚故受水。若先有水在器中。则安得复受水乎。故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虚受人。论语称夫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夫子曰。无适也。无莫也。惟义与比。此皆虚中无我之谓也。欲学大舜之孝。当先学其德为圣人。欲学其德为圣人。当先学其取人为善。欲学其取人为善。当先克去一我字。伏愿 殿下于一我字上。深加省察而用力克去焉。 上曰。其言好矣。经筵官进来。元震进伏。 上曰。昼讲时经筵官入参之意下教矣。今此入参。眷眷晋讲。诚为嘉悦。而第经筵官不可以爵禄縻之。只当以诚信待之。然山野之人。玉署之窠。则虽无出入之事。春坊之官。则多有出入之例矣。以贾谊上疏言之。辅翊太子为先。当今第一急务。专在于辅导元良也。 列
中庸孟子。必以好问好察取人为善称之何哉。盖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一人之聪明有限。故非好问好察。取人为善。则无以尽天下之善而有诸己也。此其好问好察。取人为善。其度量之大。功效之至。非资质之美所得以比也。然取人为善。只在于去一我字。若于心下。先容着一我字。则无以复容他人之言矣。天下之善。安得以复至乎。譬之镜虚故照物。若先有一物在镜中。则安得复照物也。器虚故受水。若先有水在器中。则安得复受水乎。故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虚受人。论语称夫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夫子曰。无适也。无莫也。惟义与比。此皆虚中无我之谓也。欲学大舜之孝。当先学其德为圣人。欲学其德为圣人。当先学其取人为善。欲学其取人为善。当先克去一我字。伏愿 殿下于一我字上。深加省察而用力克去焉。 上曰。其言好矣。经筵官进来。元震进伏。 上曰。昼讲时经筵官入参之意下教矣。今此入参。眷眷晋讲。诚为嘉悦。而第经筵官不可以爵禄縻之。只当以诚信待之。然山野之人。玉署之窠。则虽无出入之事。春坊之官。则多有出入之例矣。以贾谊上疏言之。辅翊太子为先。当今第一急务。专在于辅导元良也。 列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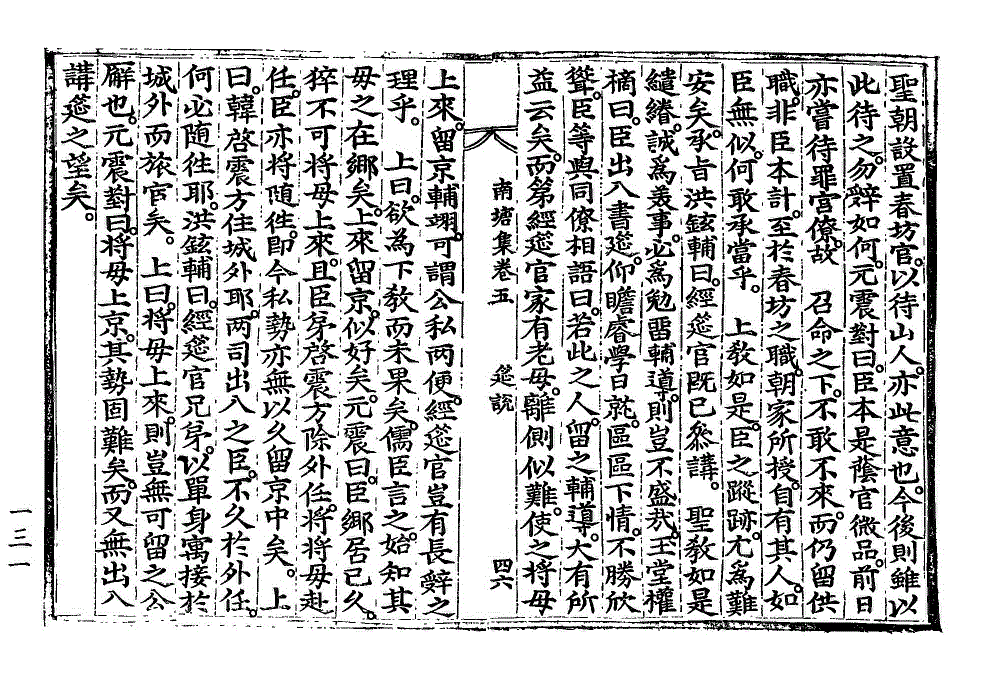 圣朝设置春坊官。以待山人。亦此意也。今后则虽以此待之。勿辞如何。元震对曰。臣本是荫官微品。前日亦尝待罪宫僚。故 召命之下。不敢不来。而仍留供职。非臣本计。至于春坊之职。朝家所授。自有其人。如臣无似。何敢承当乎。 上教如是。臣之踪迹。尤为难安矣。承旨洪铉辅曰。经筵官既已参讲。 圣教如是缱绻。诚为美事。必为勉留辅导。则岂不盛哉。玉堂权𥛚曰。臣出入书筵。仰瞻睿学日就。区区下情。不胜欣耸。臣等与同僚相语曰。若此之人。留之辅导。大有所益云矣。而第经筵官家有老母。离侧似难。使之将母上来。留京辅翊。可谓公私两便。经筵官岂有长辞之理乎。 上曰。欲为下教而未果矣。儒臣言之。始知其母之在乡矣。上来留京。似好矣。元震曰。臣乡居已久。猝不可将母上来。且臣弟启震方除外任。将将母赴任。臣亦将随往。即今私势亦无以久留京中矣。 上曰。韩启震方住城外耶。两司出入之臣。不久于外任。何必随往耶。洪铉辅曰。经筵官兄弟。以单身寓接于城外而旅宦矣。 上曰。将母上来。则岂无可留之公廨也。元震对曰。将母上京。其势固难矣。而又无出入讲筵之望矣。
圣朝设置春坊官。以待山人。亦此意也。今后则虽以此待之。勿辞如何。元震对曰。臣本是荫官微品。前日亦尝待罪宫僚。故 召命之下。不敢不来。而仍留供职。非臣本计。至于春坊之职。朝家所授。自有其人。如臣无似。何敢承当乎。 上教如是。臣之踪迹。尤为难安矣。承旨洪铉辅曰。经筵官既已参讲。 圣教如是缱绻。诚为美事。必为勉留辅导。则岂不盛哉。玉堂权𥛚曰。臣出入书筵。仰瞻睿学日就。区区下情。不胜欣耸。臣等与同僚相语曰。若此之人。留之辅导。大有所益云矣。而第经筵官家有老母。离侧似难。使之将母上来。留京辅翊。可谓公私两便。经筵官岂有长辞之理乎。 上曰。欲为下教而未果矣。儒臣言之。始知其母之在乡矣。上来留京。似好矣。元震曰。臣乡居已久。猝不可将母上来。且臣弟启震方除外任。将将母赴任。臣亦将随往。即今私势亦无以久留京中矣。 上曰。韩启震方住城外耶。两司出入之臣。不久于外任。何必随往耶。洪铉辅曰。经筵官兄弟。以单身寓接于城外而旅宦矣。 上曰。将母上来。则岂无可留之公廨也。元震对曰。将母上京。其势固难矣。而又无出入讲筵之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