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x 页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题跋
题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3H 页
 跋伊川先生上仁宗书
跋伊川先生上仁宗书昔者子路言志。见哂于夫子。岂不以为国以礼而其言不让耶。故曰能以礼让。为国从政乎何有。圣人之贵让如此。余观伊川先生年十八。上仁宗书。其自任之重。虽贲育有不可夺。其于让道。抑恐有少损。其言曰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汉武笑齐宣不行孟子之说而不用仲舒。隋文笑汉武不用仲舒之策而不听王通。二主之昏。陛下亦尝笑之矣。勿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盖王道之必可行。如谷之可食。无复致疑。然世易今古。俗尚顿别。虽三代之迭兴。犹不免有所损益。变以通之。未尝胶守往辙。岂非因时之所宜而为之制耶。道之不行殆二千岁。后儒但从古纸上寻觅。不过谈龙肉而实未得一尝。虽使猝然当之。必将有龃龉矛盾。已不胜其纷纭矣。且驱排一世。兀然独守吾所知。则其衅罅旁伺。蜂窠蚁穴。安得以防诸。是则志未及伸。迹已堕坑。将无裨于世道。而为身命之害。则有不可悔者矣。伊川能熟揣于长夜之中。独唱于众咻之间。而保无颠沛之忧耶。况又曰陛下大用之。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诚使时君为尧舜而满庭皆夔龙则其说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3L 页
 亦自良是。或恐仁宗无此力量。左右者或掣肘柅行。而毕竟罪过之难脱矣。是未可知也。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又曰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伊川又引此为證。当时亦不可谓已治矣。苟任之专而行之有术。亦奚待五年七年之久。孔子亦尝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期月云者。谓救焚拯溺。一岁之周而民已有赖其泽者。三年云者。谓纲纪稍立。政令有统。而为治邦之根基。可以从此行去也。然孔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何也。此圣人斟量轻重。灼见始卒。如耕之终亩。织之成匹。虽欲趱急而有不可得。盖天下之人心。未可尽革。耳目既惯。习俗既成。在下之小人。虽可使革面从化。而居位贵显者。未可一以齐之也。至三十年则幼者壮。老者死。世已易矣。于是乎渐摩浸染。革旧图新。庶几熙皞之域。而圣人之能事毕矣。朱子尝引周宣干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要罢三十年科举始得。此言极好。此亦不世不变之意。且如渫井。井中元有十斛浊水。上面去一斛浊。下面便有一斛清来和。二斛三斛亦然。虽去尽十斛。而犹是半浊之水。至渫之不已。尘滓渐除。积久而方得十分清。教化之于世道亦如此。以是知俗之难变有如此者。孟子伊川之说。亦只是大槩言之也欤。
亦自良是。或恐仁宗无此力量。左右者或掣肘柅行。而毕竟罪过之难脱矣。是未可知也。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又曰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伊川又引此为證。当时亦不可谓已治矣。苟任之专而行之有术。亦奚待五年七年之久。孔子亦尝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期月云者。谓救焚拯溺。一岁之周而民已有赖其泽者。三年云者。谓纲纪稍立。政令有统。而为治邦之根基。可以从此行去也。然孔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何也。此圣人斟量轻重。灼见始卒。如耕之终亩。织之成匹。虽欲趱急而有不可得。盖天下之人心。未可尽革。耳目既惯。习俗既成。在下之小人。虽可使革面从化。而居位贵显者。未可一以齐之也。至三十年则幼者壮。老者死。世已易矣。于是乎渐摩浸染。革旧图新。庶几熙皞之域。而圣人之能事毕矣。朱子尝引周宣干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要罢三十年科举始得。此言极好。此亦不世不变之意。且如渫井。井中元有十斛浊水。上面去一斛浊。下面便有一斛清来和。二斛三斛亦然。虽去尽十斛。而犹是半浊之水。至渫之不已。尘滓渐除。积久而方得十分清。教化之于世道亦如此。以是知俗之难变有如此者。孟子伊川之说。亦只是大槩言之也欤。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4H 页
 跋朱子答曾无疑书
跋朱子答曾无疑书此书所论。必指主丧者不成服。而丧所并阙奠馈。延至累月之久。而人情有不得不然者也。恐非谓壹是皆如此也。凡丧在此月而服成于后月。丧在此岁而服成于后岁。又或家贫不能办庀。延过十数日。至于后月而服成者。其练丧及除服。未闻有从成服日数起者。此何异例。然则成服虽曰太晚。若成于月中而不至久延者。宜准贫家久而方成之例。练丧及除服皆从丧日。设若延至累月之久。服衰日短。人情不近。却宜准此书所论从成服日数起也。至于练祥。其并阙奠馈者。宜亦准此书所论。而其不然者岂可因除服之故。而无端延久不举乎。死者之丧。生者之服。自是两般。故曰祭不为除丧设。此则前已备论矣。或疑主人不练服而犹举期祭则练为虚名。此盖以常道言也。期而当练。以名其祭。或事变而当练不练。不之计也。纵曰主丧者不练其服。岂非当练之期乎。若必欲从主丧之服而方举二祥。则是丧或有四年五年之久。而又或有既毕还设者矣。岂非惑乎。
跋欧阳公春秋论
按诸侯立而未逾年则称子。犹不成为君也。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子般卒。般已立而卒。以其未逾年。故不得为继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4L 页
 世之主。意者当时之礼。君薨子虽代总国事。而至于即位则必待逾年。故未逾年不称元年。而子而已矣。若君薨子便即位则已成君也。其逾年与否。不必言。春秋信史也。分明道春王正月即位。若先已即位。孔子缘何而昧然至明年始书乎。昭公薨。其明年正月。即定公元年正月。而定公以六月即位。故亦据实以书之。以是知皆正月即位也。左传云子般即位。次于党氏。然则当时亦或有未逾年而即位者。以其一时之权宜。非定礼。故春秋不许。夫即位。国之大事。苟其定礼也。则虽般之即位。不容不书。过则有定公。不及则有般。而书法异例。以是益知逾年者为正法也。春秋之际。乱贼接踵。事变叵测。权臣各援所厚。争为己功。其势有不待逾年矣。若然者。至明年正月遂无事。假使般不见弑而仍为继世之主。则其元年正月。必无即位之书也。如隐庄闵僖之不书即位。何以异哉。然则四公者。其必不待逾年者。而春秋讳之也。般亦岂突然独刱也乎。春秋十二世之间。必有行之如般者。而今得元年无即位止于四公。则以此为断。或者近之乎。史记秦世家孝文王立。至明年十月始即位。盖当时此礼已废。而孝文独行之也。胡氏传曰内不承于先君。上不禀于天子。诸大夫援己而立。争乱造端。故仲尼削之。若然春秋可削者何限。而独于数君
世之主。意者当时之礼。君薨子虽代总国事。而至于即位则必待逾年。故未逾年不称元年。而子而已矣。若君薨子便即位则已成君也。其逾年与否。不必言。春秋信史也。分明道春王正月即位。若先已即位。孔子缘何而昧然至明年始书乎。昭公薨。其明年正月。即定公元年正月。而定公以六月即位。故亦据实以书之。以是知皆正月即位也。左传云子般即位。次于党氏。然则当时亦或有未逾年而即位者。以其一时之权宜。非定礼。故春秋不许。夫即位。国之大事。苟其定礼也。则虽般之即位。不容不书。过则有定公。不及则有般。而书法异例。以是益知逾年者为正法也。春秋之际。乱贼接踵。事变叵测。权臣各援所厚。争为己功。其势有不待逾年矣。若然者。至明年正月遂无事。假使般不见弑而仍为继世之主。则其元年正月。必无即位之书也。如隐庄闵僖之不书即位。何以异哉。然则四公者。其必不待逾年者。而春秋讳之也。般亦岂突然独刱也乎。春秋十二世之间。必有行之如般者。而今得元年无即位止于四公。则以此为断。或者近之乎。史记秦世家孝文王立。至明年十月始即位。盖当时此礼已废。而孝文独行之也。胡氏传曰内不承于先君。上不禀于天子。诸大夫援己而立。争乱造端。故仲尼削之。若然春秋可削者何限。而独于数君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5H 页
 不贷至此乎。彼数君者。鲁之先君。削之罪之也。圣人其肯乎此耶。今观欧阳氏所论。其从经舍传。以隐公为非摄则尽有见矣。若但曰阙其所不知则大不然。惠公之终。隐公之始。果有不可考。而其元年正月即位。岂不知而阙者耶。且如庄闵僖有何不详其始终而然乎。欧阳氏又论赵盾许止。大槩得之。昔者孟孙问孝。孔子答以无违。既而语樊迟以发之。樊迟欲学稼。答以不如农圃。既又语门人以发之。盖惧夫未谕其本旨也。彼两人者。若本无弑君之心。因偶有所未尽而严诛至此。不复发其所以诛。则百世之下。其有能识得本旨者乎。其于防杜乱贼之心则固周密矣。而独于两人无戴盆之冤乎。杀一不辜而有天下。君子不为。今为天下之乱贼而任弃无辜之人。加之穷凶之恶名。是可忍耶。圣人既书曰弑则必有知其罪而罪之也。其弑之迹。今不可考。而杀人以法者。毕竟与挺刃无别。盾不越境则是以不越境弑者也。止不尝药则是以不尝药弑者也。是谓弑君以法而不以挺刃者也。君子谓止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夫药物所以济死。礼君父有疾。臣子必先尝之。如之何可舍。以不可舍而谓之可舍。意厚而言正。所以为君子也。公谷谬曰不弑。遂实之以嗌不容粒。既与左氏奔晋者不合。则未必其无讹。借曰有之。人之情伪
不贷至此乎。彼数君者。鲁之先君。削之罪之也。圣人其肯乎此耶。今观欧阳氏所论。其从经舍传。以隐公为非摄则尽有见矣。若但曰阙其所不知则大不然。惠公之终。隐公之始。果有不可考。而其元年正月即位。岂不知而阙者耶。且如庄闵僖有何不详其始终而然乎。欧阳氏又论赵盾许止。大槩得之。昔者孟孙问孝。孔子答以无违。既而语樊迟以发之。樊迟欲学稼。答以不如农圃。既又语门人以发之。盖惧夫未谕其本旨也。彼两人者。若本无弑君之心。因偶有所未尽而严诛至此。不复发其所以诛。则百世之下。其有能识得本旨者乎。其于防杜乱贼之心则固周密矣。而独于两人无戴盆之冤乎。杀一不辜而有天下。君子不为。今为天下之乱贼而任弃无辜之人。加之穷凶之恶名。是可忍耶。圣人既书曰弑则必有知其罪而罪之也。其弑之迹。今不可考。而杀人以法者。毕竟与挺刃无别。盾不越境则是以不越境弑者也。止不尝药则是以不尝药弑者也。是谓弑君以法而不以挺刃者也。君子谓止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夫药物所以济死。礼君父有疾。臣子必先尝之。如之何可舍。以不可舍而谓之可舍。意厚而言正。所以为君子也。公谷谬曰不弑。遂实之以嗌不容粒。既与左氏奔晋者不合。则未必其无讹。借曰有之。人之情伪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5L 页
 有不可尽测。若果即其自责而责之则君子好谦反咎。必将多取恶名。而眚灾肆赦者为虚语矣。又况止之意本欲自责而免乎弑君之名也。在止宁恬然而不反咎之为愈耶。其言之不足信如此。至于盾。左氏于是乎曲笔矣。其记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夫以实之谓不隐。彼既不隐则此当有实。虽使越境。乌得以免哉。且手弑者穿也。圣人既知盾之无妄。而急于归狱。不顾穿之漏网。宁有是耶。公羊云灵公呼獒而属之。祈弥明踆之。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信斯言也。其奸萌已于此而不可折矣。盾不幸而遭变。既不能死。则将遁逃畏避之不暇。而仓卒之际。肆然哃喝。誇己之有獒。果然君獒不敢杀盾。而盾之獒则穿也。故盾之出宫门。便是属獒之辰也。其谁曰弑夷皋者。獒也。非盾也。
有不可尽测。若果即其自责而责之则君子好谦反咎。必将多取恶名。而眚灾肆赦者为虚语矣。又况止之意本欲自责而免乎弑君之名也。在止宁恬然而不反咎之为愈耶。其言之不足信如此。至于盾。左氏于是乎曲笔矣。其记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夫以实之谓不隐。彼既不隐则此当有实。虽使越境。乌得以免哉。且手弑者穿也。圣人既知盾之无妄。而急于归狱。不顾穿之漏网。宁有是耶。公羊云灵公呼獒而属之。祈弥明踆之。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信斯言也。其奸萌已于此而不可折矣。盾不幸而遭变。既不能死。则将遁逃畏避之不暇。而仓卒之际。肆然哃喝。誇己之有獒。果然君獒不敢杀盾。而盾之獒则穿也。故盾之出宫门。便是属獒之辰也。其谁曰弑夷皋者。獒也。非盾也。跋刘共父行状
朱子代刘玶述其本生兄珙行状。末乃题曰从弟玶谨状。后人咸以此为据。凡本生父母兄弟。皆作从子从兄弟之称。已成通行之礼。以愚观之。实有可疑何也。玶出后于其季父则于属为从弟也。从兄弟相为服大功。而兄弟之出后者亦大功。则其制服亦等也。设若出后于再从三从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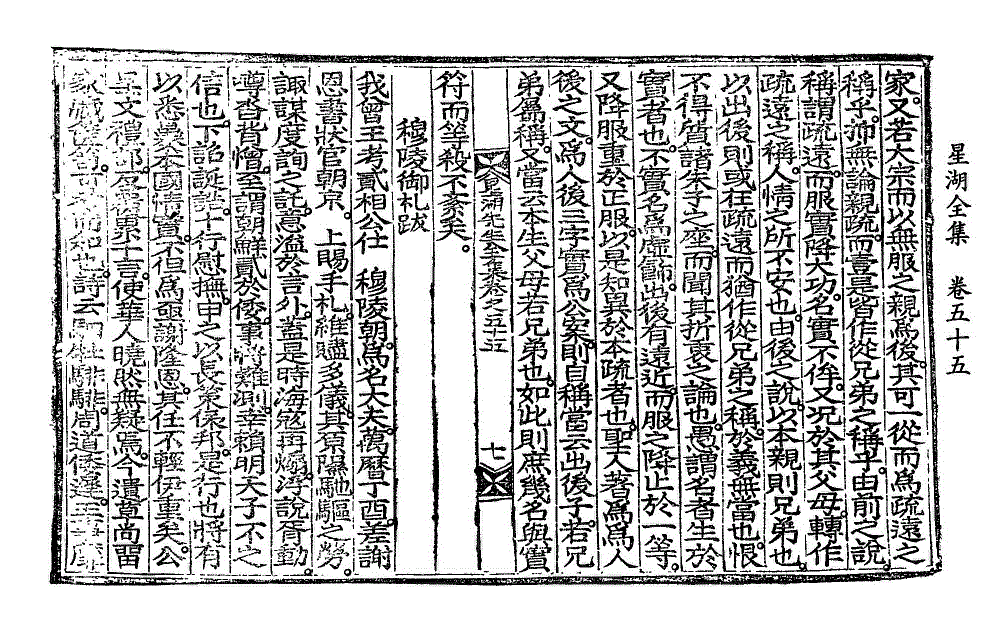 家。又若大宗而以无服之亲为后。其可一从而为疏远之称乎。抑无论亲疏。而壹是皆作从兄弟之称乎。由前之说。称谓疏远。而服实降大功。名实不侔。又况于其父母。转作疏远之称。人情之所不安也。由后之说。以本亲则兄弟也。以出后则或在疏远而犹作从兄弟之称。于义无当也。恨不得质诸朱子之座。而闻其折衷之论也。愚谓名者生于实者也。不实名为虚饰。出后有远近。而服之降止于一等。又降服重于正服。以是知异于本疏者也。圣人著为为人后之文。为人后三字实为公案。则自称当云出后子。若兄弟属称。又当云本生父母若兄弟也。如此则庶几名与实符而等杀不紊矣。
家。又若大宗而以无服之亲为后。其可一从而为疏远之称乎。抑无论亲疏。而壹是皆作从兄弟之称乎。由前之说。称谓疏远。而服实降大功。名实不侔。又况于其父母。转作疏远之称。人情之所不安也。由后之说。以本亲则兄弟也。以出后则或在疏远而犹作从兄弟之称。于义无当也。恨不得质诸朱子之座。而闻其折衷之论也。愚谓名者生于实者也。不实名为虚饰。出后有远近。而服之降止于一等。又降服重于正服。以是知异于本疏者也。圣人著为为人后之文。为人后三字实为公案。则自称当云出后子。若兄弟属称。又当云本生父母若兄弟也。如此则庶几名与实符而等杀不紊矣。穆陵御札跋
我曾王考贰相公仕 穆陵朝。为名大夫。万历丁酉。差谢恩书状官朝京。 上赐手札。维赆多仪。其原隰驰驱之劳。诹谋度询之托。意溢于言外。盖是时海寇再煽。浮说胥动。噂沓背憎。至谓朝鲜贰于倭。事将难测。幸赖明天子不之信也。下诏诞诰。十行慰抚。申之以长策保邦。是行也将有以悉㬥本国情实。不但为亟谢隆恩。其任不轻伊重矣。公呈文礼部。反覆累千言。使华人晓然无疑焉。今遗草尚留家藏箧笥。可考而知也。诗云驷牡騑騑。周道倭迟。王事靡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6L 页
 盬。我心伤悲。当时昭融契合尽节报效。于此亦可以想像万一。再从侄观休习于家传旧事。收拾以妆帖。故敬书其后。
盬。我心伤悲。当时昭融契合尽节报效。于此亦可以想像万一。再从侄观休习于家传旧事。收拾以妆帖。故敬书其后。陶山道脉帖跋
陶山道脉帖者。李仲宾之所集也。以退溪为首。其诸门人西厓以下显名及后来旅轩,愚伏诸贤。咸在编列。而惟取简牍。盖东方儒术之盛。后退溪而无退溪也。先生之殁。殆近二百年。而执经者莫不祖此。比如君子垂荫。孱孙弥远。典则虽替。而其故家馀俗。往往犹有可徵。故由今日追仰景慕。如末裔之尊祖。当时及门亲炙诸公。又有似乎族姓之尊属。裒然可敬。其手泽精彩。于斯不泯。合以观之。必将有油然感兴矣。然则此帖便是宗门世谱。而于儒者事不为无助。但恨其世无适孙行耳。
跋五贤录
余从洪君某甫游。某甫示余其伯氏公所辑五贤录者。余览而知用意之不易也。夫思其人不见。必欲得写影之肖似也。其体肤毛发之间。一分有未该则莫不为之咨嗟叹惜。慕之至也。况其言行之可则可像。比彼体肤毛发。已大矣。一事不举则一理有阙。其流风馀韵。幸而未泯者。在后学。宁可不尽心乎。世之记载五先生实迹。亦颇有之。今合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7H 页
 聚成帙者此录也。公于是有功。余昔过陶山。访李先生遗居。徘徊抚想。不能自已。虽杖几之间。尘蠹之馀。必详识而谨书。归而藏在巾笥。时复阅之。恍然起一月春风意思。今见此录。益有江汉羹墙之感云尔。
聚成帙者此录也。公于是有功。余昔过陶山。访李先生遗居。徘徊抚想。不能自已。虽杖几之间。尘蠹之馀。必详识而谨书。归而藏在巾笥。时复阅之。恍然起一月春风意思。今见此录。益有江汉羹墙之感云尔。跋南冥言行录
南冥先生。高尚之士也。其言槩多高苦而伤刻。谓郑圃隐一死可笑。仕恭悯三十年不去。以辛朝为王出也。则佗日放出。己亦豫焉。十年服事。一朝放杀。后日之死。深可未晓。此废心论迹之说。未有得其实也。圃隐为丽氏死。其于圣朝为何如。而开国十年。便加褒崇。此圣朝之睹记而心赏之也。至今世远事湮之后。依俙立论。臆断其得失。或者过耶。退溪之言曰世之好议论喜攻发。不乐成人之美者。哓哓不已。每欲掩耳而不闻。后圃隐而知其所存者。惟退溪耳。李宏仲记善录。录退溪之言曰当时继立者虽辛氏。而王氏宗社未亡。故犹事之如此。如牛氏继立而纲目不斥王导。正得此义。此恐记者之误也。其或先生难于为说。而微辞托言耶。夫牛继马。后来史笔所断。非当时公诵如此。若真如晋氏嗣绝则徒诿其宗社之未毁。而区区縻禄于异姓之朝。岂义之当然乎。彼王导特一贼臣。本无与国存亡之志。纲目不贬。未必为宗社之不亡。安得比而同之。且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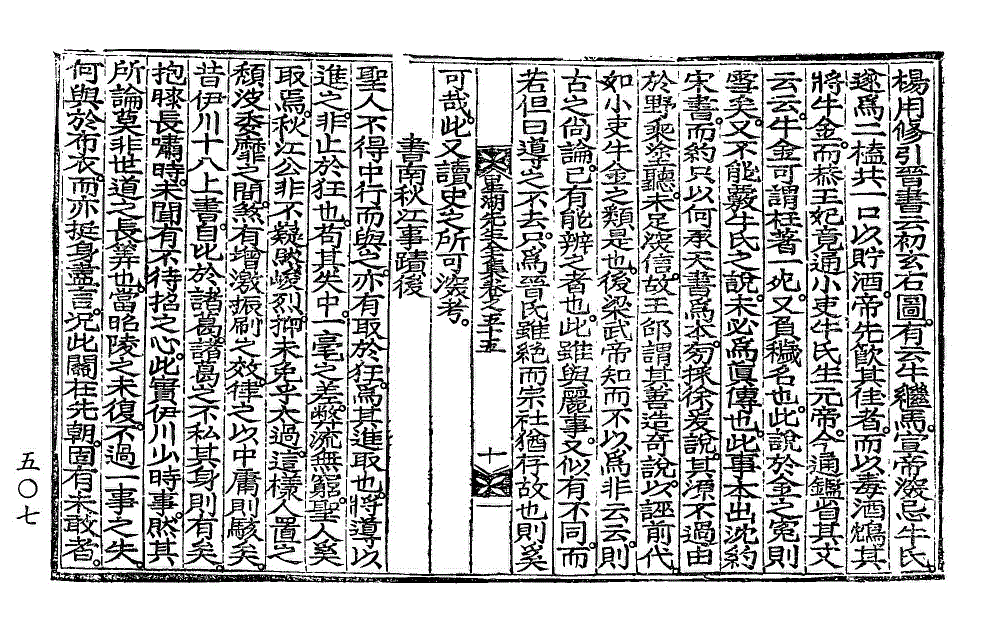 杨用修引晋书云初玄石图。有云牛继马。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其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竟通小吏牛氏生元帝。今通鉴省其文云云。牛金可谓枉著一死。又负秽名也。此说于金之冤则雪矣。又不能覈牛氏之说。未必为真传也。此事本出沈约宋书。而约只以何承天书为本。旁采徐爰说。其源不过由于野乘涂听。未足深信。故王邵谓其善造奇说。以诬前代。如小吏牛金之类是也。后梁武帝知而不以为非云云。则古之尚论。已有能辨之者也。此虽与丽事。又似有不同。而若但曰导之不去。只为晋氏虽绝而宗社犹存故也则奚可哉。此又读史之所可深考。
杨用修引晋书云初玄石图。有云牛继马。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其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竟通小吏牛氏生元帝。今通鉴省其文云云。牛金可谓枉著一死。又负秽名也。此说于金之冤则雪矣。又不能覈牛氏之说。未必为真传也。此事本出沈约宋书。而约只以何承天书为本。旁采徐爰说。其源不过由于野乘涂听。未足深信。故王邵谓其善造奇说。以诬前代。如小吏牛金之类是也。后梁武帝知而不以为非云云。则古之尚论。已有能辨之者也。此虽与丽事。又似有不同。而若但曰导之不去。只为晋氏虽绝而宗社犹存故也则奚可哉。此又读史之所可深考。书南秋江事迹后
圣人不得中行而与之。亦有取于狂。为其进取也。将导以进之。非止于狂也。苟其失中。一毫之差。弊流无穷。圣人奚取焉。秋江公非不嶷然峻烈。抑未免乎太过。这样人置之颓波委靡之间。煞有增激振刷之效。律之以中庸则骇矣。昔伊川十八上书。自比于诸葛。诸葛之不私其身则有矣。抱膝长啸时。未闻有不待招之心。此实伊川少时事。然其所论莫非世道之长算也。当昭陵之未复。不过一事之失。何与于布衣。而亦挺身尽言。况此关在先朝。固有未敢者。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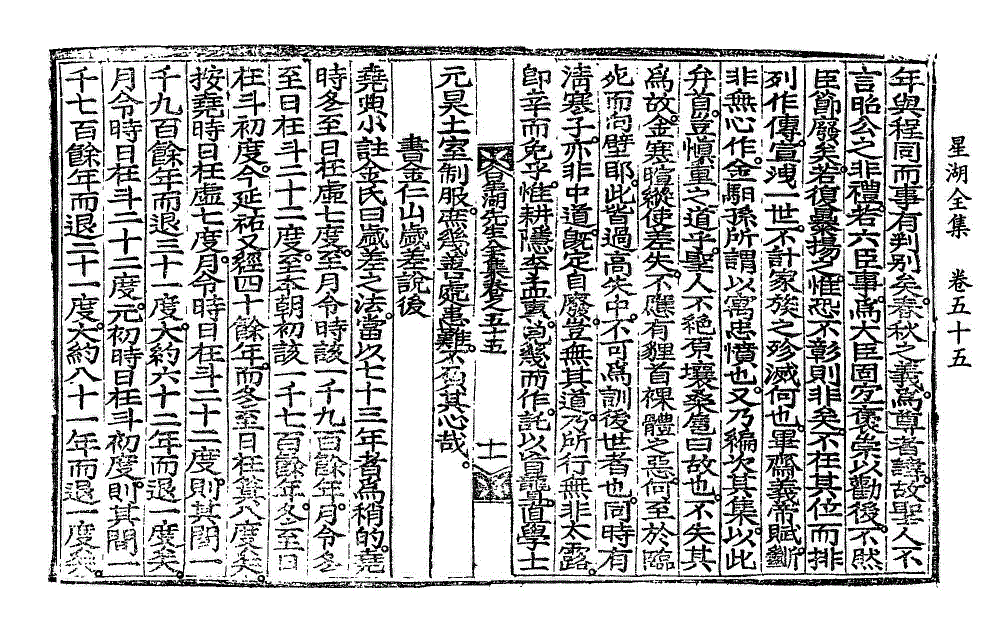 年与程同而事有判别矣。春秋之义。为尊者讳。故圣人不言昭公之非礼。若六臣事。为大臣固宜褒崇以劝后。不然臣节废矣。若复㬥扬之。惟恐不彰则非矣。不在其位而排列作传。宣泄一世。不计家族之殄灭何也。毕斋义帝赋。断非无心作。金驲孙所谓以寓忠愤也。又乃编次其集。以此弁首。岂慎重之道乎。圣人不绝原壤桑扈曰故也。不失其为故。金寒暄纵使差失。不应有狸首裸体之恶。何至于临死而向壁耶。此皆过高失中。不可为训后世者也。同时有清寒子。亦非中道。既定自废。岂无其道。乃所行无非太露。即幸而免乎。惟耕隐李孟专。见几而作。托以盲聋。直学士元昊土室制服。庶几善处患难。不负其心哉。
年与程同而事有判别矣。春秋之义。为尊者讳。故圣人不言昭公之非礼。若六臣事。为大臣固宜褒崇以劝后。不然臣节废矣。若复㬥扬之。惟恐不彰则非矣。不在其位而排列作传。宣泄一世。不计家族之殄灭何也。毕斋义帝赋。断非无心作。金驲孙所谓以寓忠愤也。又乃编次其集。以此弁首。岂慎重之道乎。圣人不绝原壤桑扈曰故也。不失其为故。金寒暄纵使差失。不应有狸首裸体之恶。何至于临死而向壁耶。此皆过高失中。不可为训后世者也。同时有清寒子。亦非中道。既定自废。岂无其道。乃所行无非太露。即幸而免乎。惟耕隐李孟专。见几而作。托以盲聋。直学士元昊土室制服。庶几善处患难。不负其心哉。书金仁山岁差说后
尧典小注金氏曰岁差之法。当以七十三年者为稍的。尧时冬至日在虚七度。至月令时该一千九百馀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本朝初该一千七百馀年。冬至日在斗初度。今延祐又经四十馀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按尧时日在虚七度。月令时日在斗二十二度。则其间一千九百馀年而退三十一度。大约六十二年而退一度矣。月令时日在斗二十二度。元初时日在斗初度。则其间一千七百馀年而退二十一度。大约八十一年而退一度矣。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8L 页
 元初日在斗初度。延祐时日在箕八度。则其间四十馀年而退四度。大约十年而退一度矣。其年数之长短。太不相侔。必有误字。不可究矣。然自唐尧元年甲辰。至延祐元年甲寅。合为三千六百七十一年。其间槩退五十六度。总计之则不过大约六十五年而退一度矣。朱子引刘焯说以七十五年为近之。金氏以七十三年为稍的。未知何据而云。
元初日在斗初度。延祐时日在箕八度。则其间四十馀年而退四度。大约十年而退一度矣。其年数之长短。太不相侔。必有误字。不可究矣。然自唐尧元年甲辰。至延祐元年甲寅。合为三千六百七十一年。其间槩退五十六度。总计之则不过大约六十五年而退一度矣。朱子引刘焯说以七十五年为近之。金氏以七十三年为稍的。未知何据而云。书启蒙翼传
按启蒙为老阳者十二。为少阳者二十。为老阴者四。为少阴者二十八。阴阳各三十二。是则适均。而占者只观其动爻。老阴比老阳为三分居一。凡阴阳画各百九十二。虽曰迭见无定。其大数则可见。其得占阴爻者。盖亦三分居一也。固是可疑。且二老合十六。二少合四十八。老比于少亦三分居一。卦有六画。槩以揣之。一卦之内。动画居二。宜乎乱动者多也。此皆未深谕。
朱子占法。每卦六十四变。与焦贡易林合。虽若奇妙。韩邦奇已有非之之论而退溪从之。以愚观之更有可疑。如乾之姤。初爻变固占勿用之象。又如之遁之讼之巽之鼎之大过。虽曰以上爻为主。而亦许下爻之同占。则其占勿用之象者六也。又如自他卦来者。自复自遁自讼自巽自鼎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9H 页
 自大过者。亦皆以勿用之象为主。凡十二占同占此象。其吉凶趋避果同乎。虽曰用之极广而其实不然也。子曰知者观其彖辞。思过半矣。彖也者。凡占皆可以占也。何独六爻不变六爻皆变及三爻变而后可占也。若乾之坤而不可占乾彖。则恐与夫子之意不合。如左传艮八既占其彖则吾未见其左契也。
自大过者。亦皆以勿用之象为主。凡十二占同占此象。其吉凶趋避果同乎。虽曰用之极广而其实不然也。子曰知者观其彖辞。思过半矣。彖也者。凡占皆可以占也。何独六爻不变六爻皆变及三爻变而后可占也。若乾之坤而不可占乾彖。则恐与夫子之意不合。如左传艮八既占其彖则吾未见其左契也。易始于伏羲。其始必首乾。意者伏羲建子为天统矣。纬书亦云伏羲建子。神农建丑。黄帝建寅。夏后氏宗黄帝。殷人宗神农。周人宗伏羲。今以三易之说推之。理或有之。又以尚书月正元日之类推之。尧舜之世。亦建寅为人统。其亦循用连山之易欤。是未可知。周虽天统。而其平王以前见于六艺之文者。莫不因夏月之名。则西周建正。不过损益行政之制。只数从此起。非易时月之名也。夏商之易。疑亦类此。若统于地则其服色官名之类。皆主于坤。统于寅则服色官名之类。皆主于艮云尔。岂有数易之卦而先坤先艮之理乎。记所谓坤乾者。愚未敢深信。或疑此指泰卦而言。此安知其必非乎。
费直之易文王周公之辞。则只书于画卦之下。自十翼以下。但以一传字加之而无彖象文言曰字。疑古易如此。然初上九六二用之语。决非后人之杜撰。而费易亦阙此。非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09L 页
 古之全文明矣。今各附传文。虽曰郑王诸儒之失。而于乾卦可见古文次序也。先之以文王。次之以周公。然后以十翼附之。以见辞之先后。自坤以下。方各自附传。以便观览。其意亦详尽矣。
古之全文明矣。今各附传文。虽曰郑王诸儒之失。而于乾卦可见古文次序也。先之以文王。次之以周公。然后以十翼附之。以见辞之先后。自坤以下。方各自附传。以便观览。其意亦详尽矣。易举正见于洪迈所录只数十条。余于陶九成说郛得见全书。盖马端临福州道藏中所见者是也。合为百三条。间多有极有理者不可泯也。今大传中既济彖传注。只采一条。则其馀并在所弃矣。意者易解既经程朱之定论。则其纷纷异同。等是为儒家之所斥耶。然今文中孚彖传。鱼与虚为韵。小过小象传。上与亢为韵。恐无所误。郭氏之录。其不可专信如此。且不论郭之得失如何。易经独未遭秦火之燬。然王郑以后颠倒错简如此。据戴记经解。分明有脱简。又据先儒刊定阙文误字不啻多矣。是岂皆吕政之所为乎。宜儒术之知愧矣。
子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象动乎内。道有变动。故曰爻。爻即画之变动者也。今以不变七八之画。通谓之爻则误矣。互体之说。原于康成。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侯之筮。分明有此义。且据系辞。舍其初上。专取中爻。只言其二四三五则互体之所以起也。愚按未济初六象传极字。当从拯字为是。涣下体坎也。故初六云用拯。与此同例。而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0H 页
 拯与正为韵也。艮明夷二卦互。下体皆坎。故于九二言拯。此可为一證。周礼六诗。皆掌于太师之官。若以乐为诗之本义。而专以声律解诗。则岂不偏乎。易可以卜筮。而尚辞之类在中。诗可以为乐。而言志之类在中。乌可以尚辞言志之类。谓独非易诗之本义。圣人赞易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是岂专指卜筮而云哉。且大象者总解一卦。而其言皆非占决之意。如非礼不履。朋友讲习之类。何待占之以后知也。若果一归于卜筮则夫子十翼。亦多非本义耳。此皆可疑。
拯与正为韵也。艮明夷二卦互。下体皆坎。故于九二言拯。此可为一證。周礼六诗。皆掌于太师之官。若以乐为诗之本义。而专以声律解诗。则岂不偏乎。易可以卜筮。而尚辞之类在中。诗可以为乐。而言志之类在中。乌可以尚辞言志之类。谓独非易诗之本义。圣人赞易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是岂专指卜筮而云哉。且大象者总解一卦。而其言皆非占决之意。如非礼不履。朋友讲习之类。何待占之以后知也。若果一归于卜筮则夫子十翼。亦多非本义耳。此皆可疑。双湖论尚变之义。谓遇事之来。动以应之。必先随意所发。主在一卦。又就一卦上随意变爻。看变得何卦何爻。一如筮法而断之。遂引左传宣公六年王子伯廖及十二年智庄子两占为證。此害义之甚也。若然即后世术家风角鸟占之类。而彼尚有风鸟之所托。此又不尔。只使人臆度信口肆意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言者无准。听者不信。圣人其肯乎此耶。郑公子曼归欲为卿。无德而贪。故伯廖据丰屋蔀家之象以戒之。不过者谓其不久也。晋先縠以中军佐济河。据否臧凶之象以戒之。若以此为动尚其变则固无不可。谓随意定卦。就卦看变。一如筮法。则只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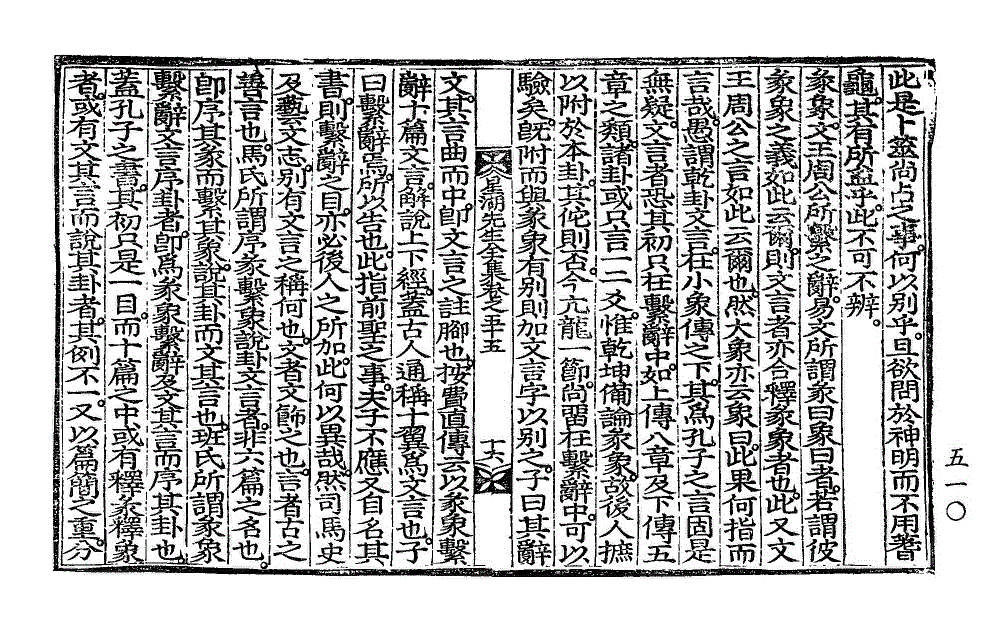 此是卜筮尚占之事。何以别乎。且欲问于神明而不用蓍龟。其有所益乎。此不可不辨。
此是卜筮尚占之事。何以别乎。且欲问于神明而不用蓍龟。其有所益乎。此不可不辨。彖象。文王周公所系之辞。易文所谓彖曰象曰者。若谓彼彖象之义如此云尔。则文言者亦合释彖象者也。此又文王周公之言如此云尔也。然大象亦云象曰。此果何指而言哉。愚谓乾卦文言。在小象传之下。其为孔子之言固是无疑。文言者恐其初只在系辞中。如上传八章及下传五章之类。诸卦或只言一二爻。惟乾坤备论彖象。故后人摭以附于本卦。其佗则否。今亢龙一节。尚留在系辞中。可以验矣。既附而与彖象有别则加文言字以别之。子曰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即文言之注脚也。按费直传云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盖古人通称十翼为文言也。子曰系辞焉。所以告也。此指前圣之事。夫子不应又自名其书。则系辞之目。亦必后人之所加。此何以异哉。然司马史及艺文志。别有文言之称何也。文者文饰之也。言者古之善言也。马氏所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者。非六篇之名也。即序其彖而系其象。说其卦而文其言也。班氏所谓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者。即为彖象系辞及文其言而序其卦也。盖孔子之书。其初只是一目。而十篇之中或有释彖释象者。或有文其言而说其卦者。其例不一。又以篇简之重。分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1H 页
 为十篇。谓之十翼。后人从而析之。有许多名目。非圣人之所知也。其所谓何谓也三字谁为也。据今系辞亢龙一节则此盖衍文。亦后人之所加也。其勿用以上爻之辞也。子曰以下。孔子之言也。其间三字。非后人之所加而何。
为十篇。谓之十翼。后人从而析之。有许多名目。非圣人之所知也。其所谓何谓也三字谁为也。据今系辞亢龙一节则此盖衍文。亦后人之所加也。其勿用以上爻之辞也。子曰以下。孔子之言也。其间三字。非后人之所加而何。杀牛不如礿祭云则知礿祭之不杀牛。文王西伯也。其祭岂有不杀牛之理。此又可證旧说之非。
经解者即小载记。小戴是汉宣帝时人。纬书出于哀平间。张衡已辨之审矣。乌可以经解为出于纬书耶。今记孔疏以为系辞文鲁直之言盖本此也。意者当时尚有可考者耶。
订易跋
人有万善。莫非天教。天非有提耳之命。示之一贯。圣神者承而辅相曰易。三百八十四爻。乃其总目。凡经礼威仪之至繁至缛。孰非其条理。故君子上达知性知天。根株枝叶。一理该通也。孔子曰我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始信小事大事舍此奚可。擿埴如吾辈。即日用而不知者。宁不愧惧。是以君子之用易。言则尚辞。动必尚变。字考句诠。反覆敬受。无殊乎函席之唯诺。庶几违道之不远。六经四子与古史之直道正行。孰非对越中流出哉。今为学之方。亦宜就前言往行。必推寻其所祖所述。彼此勘合。捃采对同。究到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1L 页
 源本而后已也。吾友洪水部锡余氏雅习于易。趋趋步步。心准意想。又溯洄黄卷。必以是印證。两相参较。合为之书。卒乃编成。名之以订易。彖象为纲。经史为目。包括极周。上自王公大人。以及闾巷夫妇。莫不涵濡在一部羲画之中。比之天出瑰宝。棋置而星罗。待人之取用。彼经若史。如夏翟之取羽。孤桐之取峄。蠙珠浮磬之取于淮泗也。锡余氏之编。如见翟而知羽。见桐而知峄。见珠磬而知淮泗。不惟用裕于己。亦知造物之所以产。如是然后亲切著己。功夫尽大矣。其规模则韩诗之外传。精彩则朱文公之通解。学易家何可以少此一著。瀷犹未夕死。幸赖此与有闻焉。
源本而后已也。吾友洪水部锡余氏雅习于易。趋趋步步。心准意想。又溯洄黄卷。必以是印證。两相参较。合为之书。卒乃编成。名之以订易。彖象为纲。经史为目。包括极周。上自王公大人。以及闾巷夫妇。莫不涵濡在一部羲画之中。比之天出瑰宝。棋置而星罗。待人之取用。彼经若史。如夏翟之取羽。孤桐之取峄。蠙珠浮磬之取于淮泗也。锡余氏之编。如见翟而知羽。见桐而知峄。见珠磬而知淮泗。不惟用裕于己。亦知造物之所以产。如是然后亲切著己。功夫尽大矣。其规模则韩诗之外传。精彩则朱文公之通解。学易家何可以少此一著。瀷犹未夕死。幸赖此与有闻焉。跋心性直指
心性直指者。皇明林兆恩之所著也。其心法有艮背行庭。其艮背心法者。背者从北从肉。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属水。故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以南方之心则火矣。火阳也。南之而居前。水阴也。北之而居后。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水之背之北者。易所谓洗心退藏于密也。五脏皆丽于背。心既背而水之则心清净矣。其行庭心法者。天之极上处至地之极下处。总八万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肾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肾之间。乃天地之间。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点灵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2H 页
 初也。时止则止。太极立焉。时行则行。周天行焉。一阴一阳。而一点之善。落于庭之中焉。成之以为性也。其阴阳妙合。以凝不测之神乎。犹一夫一妇。而一点之善。落于子宫之中焉。成之而为人也。其夫妇好合以凝。不可知之道乎。盖水火者。天地之用也。而水为生化之原。归藏之宅。故观乎一草一木。敷施见于枝叶。敛藏必在根柢。此万物之必以水为本也。是以心虽属火。其敛藏疑若归于水。故兆恩之论所以起也。以人之一身言则心属火而肾属水。然若以心为藏于肾中则不妥。故艰以求之。以南系乎北者。较勘而谓火之洗乎水。又嫌其与肾水不相干则刱为行庭之说。谓别有一物居于两间而为神化之主。夫非心非肾。此果何物居于无位之地而为性为善为灵光为不测之妙乎。天地以人为心。人身之中。又具水火心肾是也。细而推之。心肾之内。又岂无水火之理哉。肾属水而却有生化之用则火之理也。心属火而又却有寂敛之境则水之理也。一水一火。各自不离于其形质之内矣。今以灵明之心。舍其部居。艮止于背肉之中。宁有是理。气之流行。自然之运也。心之应物。灵明之体也。比如天地有流行不息之气。而又却有最灵之人居其内为之心。自成形质。不复归宿于佗物。与流行之气。苗脉不同也。心脏之在腔内。何以异哉。
初也。时止则止。太极立焉。时行则行。周天行焉。一阴一阳。而一点之善。落于庭之中焉。成之以为性也。其阴阳妙合。以凝不测之神乎。犹一夫一妇。而一点之善。落于子宫之中焉。成之而为人也。其夫妇好合以凝。不可知之道乎。盖水火者。天地之用也。而水为生化之原。归藏之宅。故观乎一草一木。敷施见于枝叶。敛藏必在根柢。此万物之必以水为本也。是以心虽属火。其敛藏疑若归于水。故兆恩之论所以起也。以人之一身言则心属火而肾属水。然若以心为藏于肾中则不妥。故艰以求之。以南系乎北者。较勘而谓火之洗乎水。又嫌其与肾水不相干则刱为行庭之说。谓别有一物居于两间而为神化之主。夫非心非肾。此果何物居于无位之地而为性为善为灵光为不测之妙乎。天地以人为心。人身之中。又具水火心肾是也。细而推之。心肾之内。又岂无水火之理哉。肾属水而却有生化之用则火之理也。心属火而又却有寂敛之境则水之理也。一水一火。各自不离于其形质之内矣。今以灵明之心。舍其部居。艮止于背肉之中。宁有是理。气之流行。自然之运也。心之应物。灵明之体也。比如天地有流行不息之气。而又却有最灵之人居其内为之心。自成形质。不复归宿于佗物。与流行之气。苗脉不同也。心脏之在腔内。何以异哉。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2L 页
 如此说者。固不足以多辨。而人只见万物之归根。或疑其水为心官之所宅。而有主肾主背之说则于道甚害。故先撮其说于上。因略加辨评焉。
如此说者。固不足以多辨。而人只见万物之归根。或疑其水为心官之所宅。而有主肾主背之说则于道甚害。故先撮其说于上。因略加辨评焉。书大明一统志
事变有难易不同等。才智亦有大小不同等。事至十分之难则惟才大十分者。方可以治之。虽有九分八分者许多。皆不能了办也。比如十仞之渊。惟勇能过十仞者可超。不然虽有百千辈。尺寸之不及。皆不免陷溺。又如治丝。其九分八分之乱者。九分八分精密者可治。至于十分之乱。一丝之错解。将愈棼而不可为矣。夫国大则才大。其故何也。天下之大。其始必将合聚众小国为大。则才智之大。非不产于小国也。小国之众。未必皆产大才。而其间一或有之。举而用焉。故天下有事则四海之内必有可以治此事者出而任之也。是以汉都长安。二百年间。许多功名。皆聚九州之产。而其为长安人者。不过谷永一人。光武都洛阳。其许多功名。皆合聚九州之产。而其为洛阳人者。不过郭贺,种皓二人。唐又都长安。亦不过韩休及滉父子,第五琦,许孟容数人为京师人。宋都于汴。亦不过向敏中,王拱辰,王圭,吕诲数人为京师人。明都北京则了然无所闻也。其馀杰钜人当大事立大业照耀千古者。莫非千万里外孤根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3H 页
 弱植。只以方寸所有而一朝遇者也。故金日磾胡貉俘虏而为汉阀阅。张九龄姜公辅。遐裔鲰生而为唐辅相。丘浚洋岛遗种而为明名臣。用人之贵才而不择地如此。且如周末列国。瓜分幅裂。战斗日起。然各能用邦内材器。亦足以弭乱兴功。其磊落伟智。可历以数也。至于我国。封疆不过千有馀里。人皆生且老于域内。知见已浅矣。中世以前。犹或远人入为宰相。此道行且灭息。轩貂莫非世卿。辅佐不外京邑。又至于今日则党分四五。名色已定。苟非所好。虽有管葛之能。不之计也。国势安得不卑。生民安得不困。余故曰达乎百世之远。通乎四海之广。其贵贵而贱才。未有甚于今日也。偶阅大明一统志。感而为说。
弱植。只以方寸所有而一朝遇者也。故金日磾胡貉俘虏而为汉阀阅。张九龄姜公辅。遐裔鲰生而为唐辅相。丘浚洋岛遗种而为明名臣。用人之贵才而不择地如此。且如周末列国。瓜分幅裂。战斗日起。然各能用邦内材器。亦足以弭乱兴功。其磊落伟智。可历以数也。至于我国。封疆不过千有馀里。人皆生且老于域内。知见已浅矣。中世以前。犹或远人入为宰相。此道行且灭息。轩貂莫非世卿。辅佐不外京邑。又至于今日则党分四五。名色已定。苟非所好。虽有管葛之能。不之计也。国势安得不卑。生民安得不困。余故曰达乎百世之远。通乎四海之广。其贵贵而贱才。未有甚于今日也。偶阅大明一统志。感而为说。跋数学启蒙
算学启蒙书。初学骤看。有不可易解。其实非启蒙也。余素不晓算家。一日偶寻到平方法。颇费心力。亦不能看透。遂意造法术以之计。数无不合。极似便易。不比算书之为艰难也。然家无佗书可考。抑恐古人必已先得。而有不待吾者矣。姑记此以备后来参验。今有平方羃四千九十六步。问为方面几何。术曰列羃四千九十六步为实。凡方法其万百之类。于当位开之。千十之类。退一位开之。故于百位下置六算为六百。以为方法。呼六六为三十六。除三千六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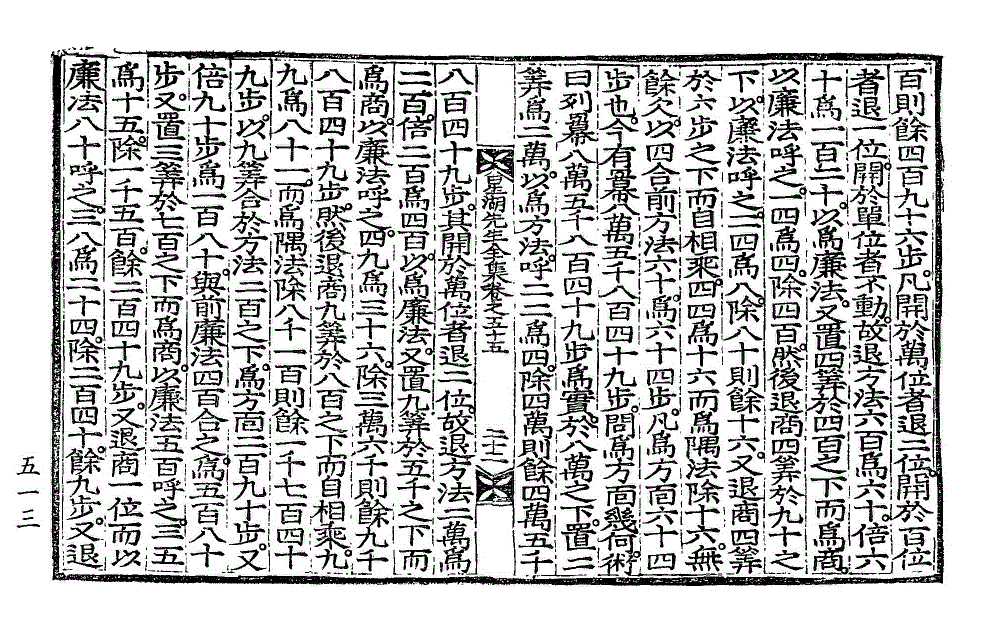 百则馀四百九十六步。凡开于万位者退二位。开于百位者退一位。开于单位者不动。故退方法六百为六十。倍六十为一百二十。以为廉法。又置四算于四百之下而为商。以廉法呼之。一四为四。除四百。然后退商四算于九十之下。以廉法呼之。二四为八。除八十则馀十六。又退商四算于六步之下而自相乘。四四为十六而为隅法除十六。无馀欠。以四合前方法六十。为六十四步。凡为方面六十四步也。今有羃八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步。问为方面几何。术曰列羃八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步为实。于八万之下。置二算为二万。以为方法。呼二二为四。除四万则馀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步。其开于万位者退二位。故退方法二万为二百。倍二百为四百。以为廉法。又置九算于五千之下而为商。以廉法呼之。四九为三十六。除三万六千则馀九千八百四十九步。然后退商九算于八百之下而自相乘。九九为八十一。而为隅法除八千一百则馀一千七百四十九步。以九算合于方法二百之下。为方面二百九十步。又倍九十步为一百八十。与前廉法四百合之。为五百八十步。又置三算于七百之下而为商。以廉法五百呼之。三五为十五。除一千五百。馀二百四十九步。又退商一位而以廉法八十呼之。三八为二十四。除二百四十。馀九步。又退
百则馀四百九十六步。凡开于万位者退二位。开于百位者退一位。开于单位者不动。故退方法六百为六十。倍六十为一百二十。以为廉法。又置四算于四百之下而为商。以廉法呼之。一四为四。除四百。然后退商四算于九十之下。以廉法呼之。二四为八。除八十则馀十六。又退商四算于六步之下而自相乘。四四为十六而为隅法除十六。无馀欠。以四合前方法六十。为六十四步。凡为方面六十四步也。今有羃八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步。问为方面几何。术曰列羃八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步为实。于八万之下。置二算为二万。以为方法。呼二二为四。除四万则馀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步。其开于万位者退二位。故退方法二万为二百。倍二百为四百。以为廉法。又置九算于五千之下而为商。以廉法呼之。四九为三十六。除三万六千则馀九千八百四十九步。然后退商九算于八百之下而自相乘。九九为八十一。而为隅法除八千一百则馀一千七百四十九步。以九算合于方法二百之下。为方面二百九十步。又倍九十步为一百八十。与前廉法四百合之。为五百八十步。又置三算于七百之下而为商。以廉法五百呼之。三五为十五。除一千五百。馀二百四十九步。又退商一位而以廉法八十呼之。三八为二十四。除二百四十。馀九步。又退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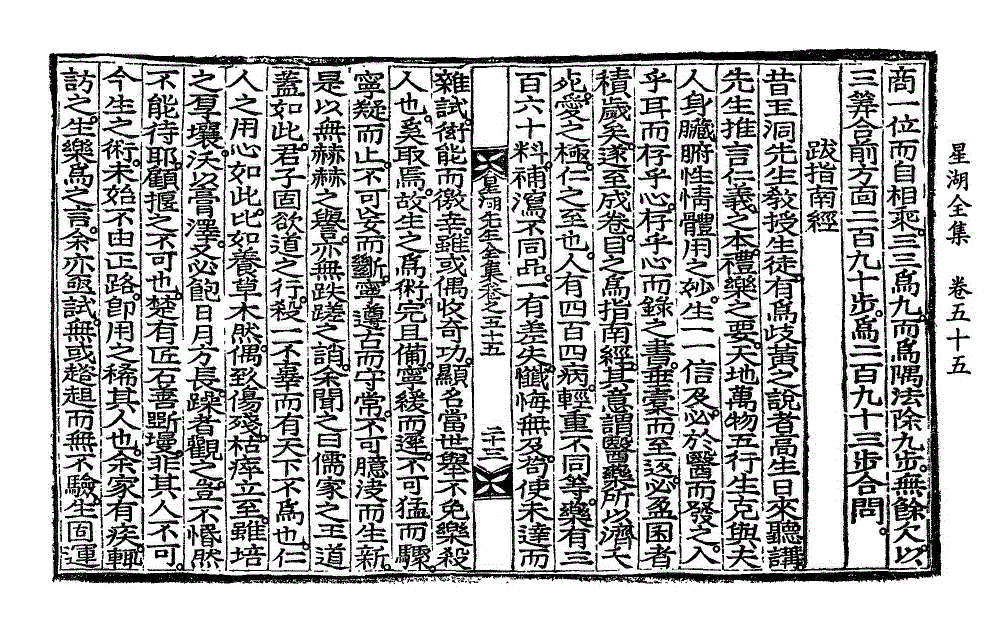 商一位而自相乘。三三为九。而为隅法除九步。无馀欠。以三算合前方面二百九十步。为二百九十三步合问。
商一位而自相乘。三三为九。而为隅法除九步。无馀欠。以三算合前方面二百九十步。为二百九十三步合问。跋指南经
昔玉洞先生教授生徒。有为歧黄之说者高生日来听讲。先生推言仁义之本。礼乐之要。天地万物五行生克与夫人身脏腑性情体用之妙。生一一信及。必于医而发之。入乎耳而存乎心。存乎心而录之书。垂橐而至返。必盈囷者积岁矣。遂至成卷。目之为指南经。其意谓医药所以济夭死。爱之极。仁之至也。人有四百四病。轻重不同等。药有三百六十料。补泻不同品。一有差失。忏悔无及。苟使未达而杂试。衒能而徼幸。虽或偶收奇功。显名当世。举不免乐杀人也。奚取焉。故生之为术。完且备。宁缓而迟。不可猛而骤。宁疑而止。不可妄而断。宁遵古而守常。不可臆决而生新。是以无赫赫之誉。亦无跌蹉之诮。余闻之曰儒家之王道盖如此。君子固欲道之行。杀一不辜而有天下不为也。仁人之用心如此。比如养草木然。偶致伤残。枯瘁立至。虽培之厚壤。沃以膏泽。又必饱日月方长。躁者观之。岂不悯然不能待耶。顾揠之不可也。楚有匠石善斲墁。非其人不可。今生之术。未始不由正路。即用之稀其人也。余家有疾。辄访之。生乐为之言。余亦亟试。无或趑趄而无不验。生固运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4L 页
 斤之巧。余亦不害为待斲之垩者欤。何其相信之深也。生间从余。谈其彝常之外。上及千古之前。远以至于九州之表。风谣物产诡怪。咸穿娓娓焉不休。言必曰玉洞子。以明师承之有自。然后知生之所存。不但一萟而止也。生袖书示余乞一言。遂识其端而还之。
斤之巧。余亦不害为待斲之垩者欤。何其相信之深也。生间从余。谈其彝常之外。上及千古之前。远以至于九州之表。风谣物产诡怪。咸穿娓娓焉不休。言必曰玉洞子。以明师承之有自。然后知生之所存。不但一萟而止也。生袖书示余乞一言。遂识其端而还之。跋职方外纪
子思子语地曰振河海而不泄。盖非海之负地。即地之载海。溟渤之外。水必有底。底者皆地。故谓收载而不泄也。子思已十分说与。而后人罔觉。及西洋之士详说以左契之。俗见犹以为讶。不可卒了也。夫地居天圆之中。不得上下。天左旋。一日一周。天之围其大几何。而能复于十二时之内。其健若此。故在天之内者。其势莫不辏以向中。今以一圆柈。置物于内。用机回转则物必推荡。至于正中而后乃已。此可验矣。故地之不得坠下。与其不得挨上。均一势也。上下四傍。皆以地为下天为上。苟使地下之。天有物坠下。则亦必至于地矣。海之丽也。如衣带之被体。四周而无不通。故西洋之士。航海穷西。毕竟复出东洋。其迤行之际。窥测星文。天顶各异。是知地底之海。亦如地上也。且北极于琼州。出地一十八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北极出地一十九度。至开平则为四十二度。琼州见南界星。开平所未见者。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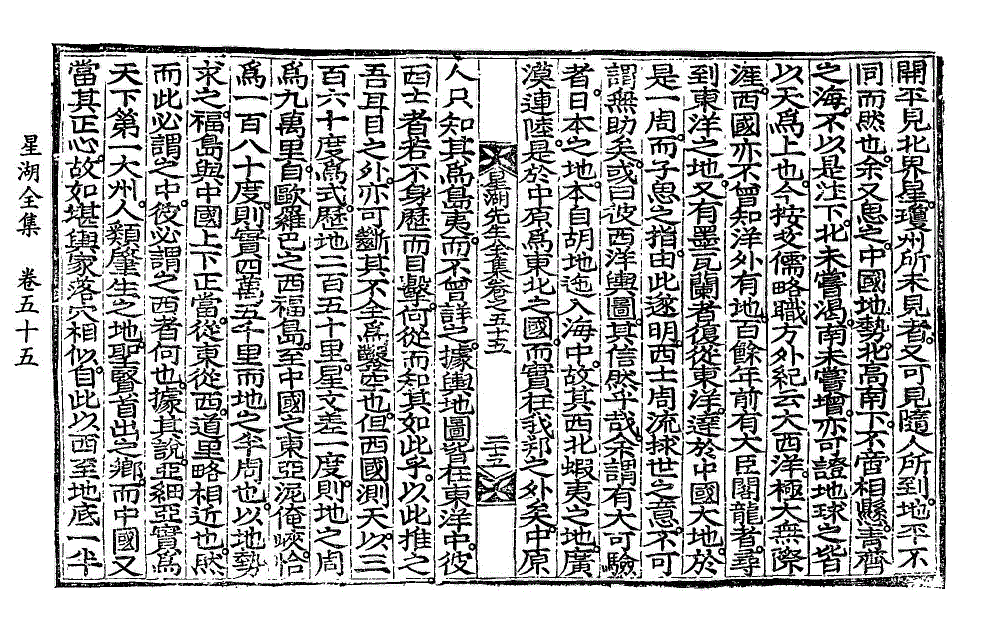 开平见北界星。琼州所未见者。又可见随人所到。地平不同而然也。余又思之。中国地势。北高南下。不啻相悬。青齐之海。不以是注下。北未尝渴。南未尝增。亦可證地球之皆以天为上也。今按艾儒略职方外纪云大西洋。极大无际涯。西国亦不曾知洋外有地。百馀年前有大臣阁龙者。寻到东洋之地。又有墨瓦兰者复从东洋。达于中国大地。于是一周。而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或曰彼西洋舆图。其信然乎哉。余谓有大可验者。日本之地。本自胡地迤入海中。故其西北虾夷之地。广漠连陆。是于中原为东北之国。而实在我邦之外矣。中原人只知其为岛夷。而不曾详之。据舆地图皆在东洋中。彼西士者若不身历而目击。何从而知其如此乎。以此推之。吾耳目之外。亦可断其不全为凿空也。但西国测天。以三百六十度为式。历地二百五十里。星文差一度。则地之周为九万里。自欧罗巴之西福岛。至中国之东亚泥俺峡。恰为一百八十度。则实四万五千里而地之半周也。以地势求之。福岛与中国上下正当。从东从西。道里略相近也。然而此必谓之中。彼必谓之西者何也。据其说。亚细亚实为天下第一大州。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而中国又当其正心。故如堪舆家落穴相似。自此以西至地底一半
开平见北界星。琼州所未见者。又可见随人所到。地平不同而然也。余又思之。中国地势。北高南下。不啻相悬。青齐之海。不以是注下。北未尝渴。南未尝增。亦可證地球之皆以天为上也。今按艾儒略职方外纪云大西洋。极大无际涯。西国亦不曾知洋外有地。百馀年前有大臣阁龙者。寻到东洋之地。又有墨瓦兰者复从东洋。达于中国大地。于是一周。而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或曰彼西洋舆图。其信然乎哉。余谓有大可验者。日本之地。本自胡地迤入海中。故其西北虾夷之地。广漠连陆。是于中原为东北之国。而实在我邦之外矣。中原人只知其为岛夷。而不曾详之。据舆地图皆在东洋中。彼西士者若不身历而目击。何从而知其如此乎。以此推之。吾耳目之外。亦可断其不全为凿空也。但西国测天。以三百六十度为式。历地二百五十里。星文差一度。则地之周为九万里。自欧罗巴之西福岛。至中国之东亚泥俺峡。恰为一百八十度。则实四万五千里而地之半周也。以地势求之。福岛与中国上下正当。从东从西。道里略相近也。然而此必谓之中。彼必谓之西者何也。据其说。亚细亚实为天下第一大州。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而中国又当其正心。故如堪舆家落穴相似。自此以西至地底一半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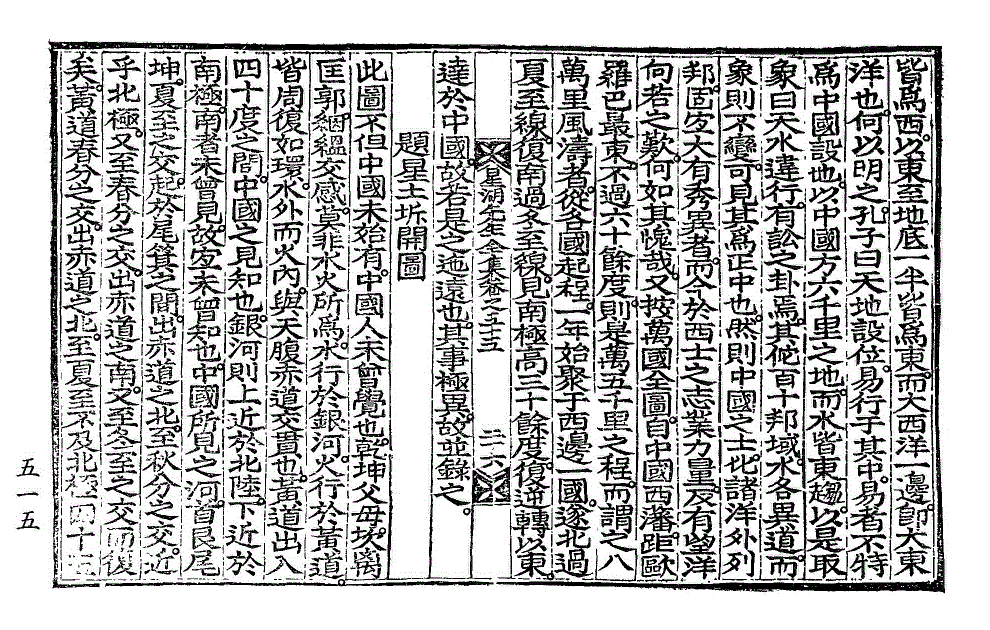 皆为西。以东至地底一半皆为东。而大西洋一边。即大东洋也。何以明之。孔子曰天地设位。易行于其中。易者不特为中国设地。以中国方六千里之地。而水皆东趋。以是取象曰天水违行。有讼之卦焉。其佗百十邦域。水各异道。而象则不变。可见其为正中也。然则中国之士。比诸洋外列邦。固宜大有秀异者。而今于西士之志业力量。反有望洋向若之叹。何如其愧哉。又按万国全图。自中国西藩。距欧罗巴最东。不过六十馀度。则是万五千里之程。而谓之八万里风涛者。从各国起程。一年始聚于西边一国。遂北过夏至线。复南过冬至线。见南极高三十馀度。复逆转以东。达于中国。故若是之迤远也。其事极异。故并录之。
皆为西。以东至地底一半皆为东。而大西洋一边。即大东洋也。何以明之。孔子曰天地设位。易行于其中。易者不特为中国设地。以中国方六千里之地。而水皆东趋。以是取象曰天水违行。有讼之卦焉。其佗百十邦域。水各异道。而象则不变。可见其为正中也。然则中国之士。比诸洋外列邦。固宜大有秀异者。而今于西士之志业力量。反有望洋向若之叹。何如其愧哉。又按万国全图。自中国西藩。距欧罗巴最东。不过六十馀度。则是万五千里之程。而谓之八万里风涛者。从各国起程。一年始聚于西边一国。遂北过夏至线。复南过冬至线。见南极高三十馀度。复逆转以东。达于中国。故若是之迤远也。其事极异。故并录之。题星土坼开图
此图不但中国未始有。中国人未曾觉也。乾坤父母。坎离匡郭。絪缊交感。莫非水火所为。水行于银河。火行于黄道。皆周复如环。水外而火内。与天腹赤道交贯也。黄道出入四十度之间。中国之见知也。银河则上近于北陆。下近于南极。南者未曾见。故宜未曾知也。中国所见之河。首艮尾坤。夏至之交。起于尾箕之间。出赤道之北。至秋分之交。近乎北极。又至春分之交。出赤道之南。又至冬至之交而复矣。黄道春分之交。出赤道之北。至夏至不及北极四十五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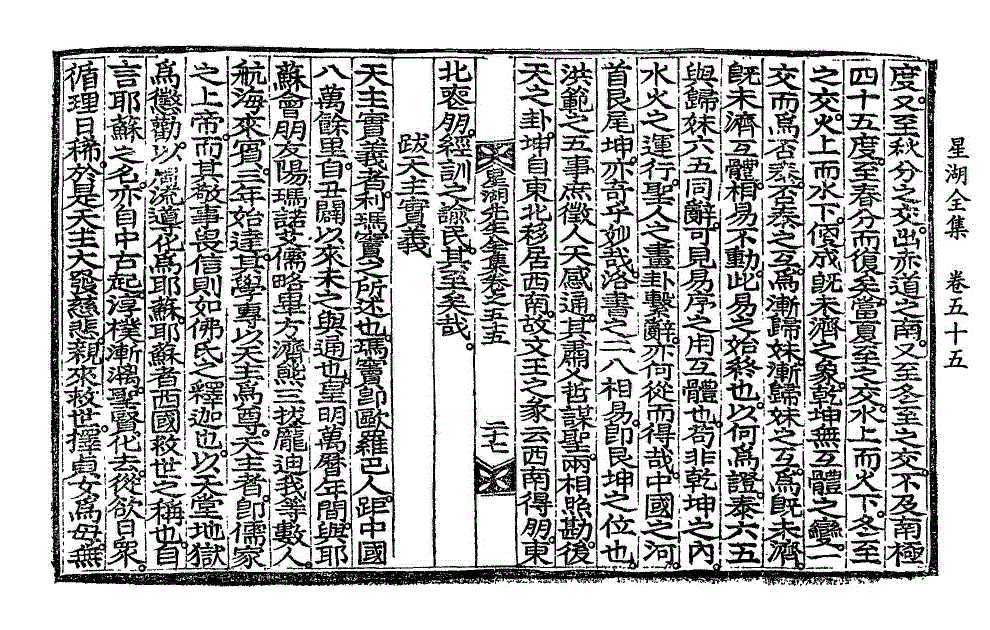 度。又至秋分之交。出赤道之南。又至冬至之交。不及南极四十五度。至春分而复矣。当夏至之交。水上而火下。冬至之交。火上而水下。便成既未济之象。乾坤无互体之变。一交而为否泰。否泰之互。为渐归妹。渐归妹之互。为既未济。既未济互体。相易不动。此易之始终也。以何为證。泰六五与归妹六五同辞。可见易序之用互体也。苟非乾坤之内。水火之运行。圣人之画卦系辞。亦何从而得哉。中国之河。首艮尾坤。亦奇乎妙哉。洛书之二八相易。即艮坤之位也。洪范之五事庶徵人天感通。其肃乂哲谋圣。两相照勘。后天之卦。坤自东北移居西南。故文王之彖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经训之谕民。其至矣哉。
度。又至秋分之交。出赤道之南。又至冬至之交。不及南极四十五度。至春分而复矣。当夏至之交。水上而火下。冬至之交。火上而水下。便成既未济之象。乾坤无互体之变。一交而为否泰。否泰之互。为渐归妹。渐归妹之互。为既未济。既未济互体。相易不动。此易之始终也。以何为證。泰六五与归妹六五同辞。可见易序之用互体也。苟非乾坤之内。水火之运行。圣人之画卦系辞。亦何从而得哉。中国之河。首艮尾坤。亦奇乎妙哉。洛书之二八相易。即艮坤之位也。洪范之五事庶徵人天感通。其肃乂哲谋圣。两相照勘。后天之卦。坤自东北移居西南。故文王之彖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经训之谕民。其至矣哉。跋天主实义
天主实义者。利玛窦之所述也。玛窦即欧罗巴人。距中国八万馀里。自丑辟以来未之与通也。皇明万历年间。与耶苏会朋友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熊三拔,庞迪我等数人。航海来宾。三年始达。其学专以天主为尊。天主者。即儒家之上帝。而其敬事畏信则如佛氏之释迦也。以天堂地狱为惩劝。以周流导化为耶苏。耶苏者西国救世之称也。自言耶苏之名。亦自中古起。淳朴渐漓。圣贤化去。从欲日众。循理日稀。于是天主大发慈悲。亲来救世。择贞女为母。无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6L 页
 所交感。托胎降生于如德亚国。名为耶苏。躬自立训。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复升归天。其教遂流及欧罗巴诸国。盖天下之大州五。中有亚细亚。西有欧罗巴。即今中国乃亚细亚中十分居一。而如德亚亦其西边一国也。耶苏之世。上距一千有六百有三年。而玛窦至中国。其朋友皆高准碧瞳。方巾青袍。初守童身。不曾有婚。朝廷官之不拜。惟日给大官之俸。习中国语。读中国书。至著书数十种。其仰观俯察。推算授时之妙。中国未始有也。彼绝域外臣。越溟海。而与学士大夫游。学士大夫莫不敛衽崇奉称先生而不敢抗。其亦豪杰之士也。然其所以斥竺乾之教者至矣。犹未觉毕竟同归于幻妄也。其书云西国古有闭他卧剌者。痛细民为恶无忌。作为轮回之说。君子断之曰其意美。其为言未免玷缺。其说遂泯。彼时此语忽漏外国。释氏图立新门。承此轮回。汉明帝闻西方有教。遣使往求。使者半道。误致身毒之国。取传中华。其或有能记前世事者。魔鬼诳人之致。是因佛教入中国之后耳。万方生死。古今所同。而佛氏之外。未有记前世一事也。中国先儒亦有此等说。唯以古今不同为證。世之牿者犹瞠焉以为疑也。今以八纮之表。同勘虚实。尤可著见之也。但中国自汉帝以前。死而还生者。并无天堂地狱之可證。则何独轮回为非。而天堂
所交感。托胎降生于如德亚国。名为耶苏。躬自立训。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复升归天。其教遂流及欧罗巴诸国。盖天下之大州五。中有亚细亚。西有欧罗巴。即今中国乃亚细亚中十分居一。而如德亚亦其西边一国也。耶苏之世。上距一千有六百有三年。而玛窦至中国。其朋友皆高准碧瞳。方巾青袍。初守童身。不曾有婚。朝廷官之不拜。惟日给大官之俸。习中国语。读中国书。至著书数十种。其仰观俯察。推算授时之妙。中国未始有也。彼绝域外臣。越溟海。而与学士大夫游。学士大夫莫不敛衽崇奉称先生而不敢抗。其亦豪杰之士也。然其所以斥竺乾之教者至矣。犹未觉毕竟同归于幻妄也。其书云西国古有闭他卧剌者。痛细民为恶无忌。作为轮回之说。君子断之曰其意美。其为言未免玷缺。其说遂泯。彼时此语忽漏外国。释氏图立新门。承此轮回。汉明帝闻西方有教。遣使往求。使者半道。误致身毒之国。取传中华。其或有能记前世事者。魔鬼诳人之致。是因佛教入中国之后耳。万方生死。古今所同。而佛氏之外。未有记前世一事也。中国先儒亦有此等说。唯以古今不同为證。世之牿者犹瞠焉以为疑也。今以八纮之表。同勘虚实。尤可著见之也。但中国自汉帝以前。死而还生者。并无天堂地狱之可證。则何独轮回为非。而天堂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7H 页
 地狱为是耶。若天主慈悲下民。现幻于寰界。间或相告语。一如人之施教。则亿万邦域。可慈可悲者何限。而一天主遍行提警。得无劳乎。自欧罗巴以东。其不闻欧罗巴之教者。又何无天主现迹。不似欧罗巴之种种灵异耶。然则其种种灵异。亦安知夫不在于魔鬼套中耶。抑又思之。鬼神者阴道也。人者阳道也。民生极炽。而神迹寝微。理即然也。以一日言则夜为阴昼为阳。故神见于夜而人作于昼。推之于一元之大。亦犹是也。其始未及生民。先有神理。逮夫民降之后。率多恍惚灵怪之事。或于传记可验。五帝三王之间。其迹犹昭昭然不可诬。善者福淫者祸。劝焉则趋。惩焉则惧。其见于诗书许多文字。定非幻语虚设。将有必然之应矣。以今论之。方当亭午之世。鬼神之理。亦已远矣。人遂委曲解之曰古所谓降祥降殃。特以理推言。初非一符于事也。殊不知古人亦据实以发之耳。何以明之。金縢圣人之书也。其祷也欲使先灵择其才艺而备使役。则定非有是理而无是应之谓也。使今俗卒然听之。岂非疑骇之甚耶。以是究之。西国风化之所由者。亦略可识取矣。意者西国之俗。亦骎骎渝变。其吉凶报应之间。渐不尊信。于是有天主经之教。其始不过如中国诗书之云。悯其犹不率也则济之以天堂地狱之说。流传至今。其后来种种灵异
地狱为是耶。若天主慈悲下民。现幻于寰界。间或相告语。一如人之施教。则亿万邦域。可慈可悲者何限。而一天主遍行提警。得无劳乎。自欧罗巴以东。其不闻欧罗巴之教者。又何无天主现迹。不似欧罗巴之种种灵异耶。然则其种种灵异。亦安知夫不在于魔鬼套中耶。抑又思之。鬼神者阴道也。人者阳道也。民生极炽。而神迹寝微。理即然也。以一日言则夜为阴昼为阳。故神见于夜而人作于昼。推之于一元之大。亦犹是也。其始未及生民。先有神理。逮夫民降之后。率多恍惚灵怪之事。或于传记可验。五帝三王之间。其迹犹昭昭然不可诬。善者福淫者祸。劝焉则趋。惩焉则惧。其见于诗书许多文字。定非幻语虚设。将有必然之应矣。以今论之。方当亭午之世。鬼神之理。亦已远矣。人遂委曲解之曰古所谓降祥降殃。特以理推言。初非一符于事也。殊不知古人亦据实以发之耳。何以明之。金縢圣人之书也。其祷也欲使先灵择其才艺而备使役。则定非有是理而无是应之谓也。使今俗卒然听之。岂非疑骇之甚耶。以是究之。西国风化之所由者。亦略可识取矣。意者西国之俗。亦骎骎渝变。其吉凶报应之间。渐不尊信。于是有天主经之教。其始不过如中国诗书之云。悯其犹不率也则济之以天堂地狱之说。流传至今。其后来种种灵异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7L 页
 之迹。不过彼所谓魔鬼诳人之致也。盖中国言其实迹。迹泯而愚者不信。西国言其幻迹。迹眩而迷者愈惑。其势然也。惟魔鬼之所以如此者。亦由天主之教。已痼人心故也。如佛法入中国。然后中国之死而复生者。能记天堂地狱及前世之事者也。彼西士之无理不穷。无幽不通。而尚不离于胶漆盆。惜哉。
之迹。不过彼所谓魔鬼诳人之致也。盖中国言其实迹。迹泯而愚者不信。西国言其幻迹。迹眩而迷者愈惑。其势然也。惟魔鬼之所以如此者。亦由天主之教。已痼人心故也。如佛法入中国。然后中国之死而复生者。能记天堂地狱及前世之事者也。彼西士之无理不穷。无幽不通。而尚不离于胶漆盆。惜哉。跋天问略
万历四十一年。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上西洋历法十四事曰。迩来台谏失职。推算日月交蚀时刻。亏分往往差谬。定朔定气。由是皆舛。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化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所未及道者。昔利玛窦最称博览。超悟其学。未传溘先朝露。今庞迪我等须发已白。年龄向衰。失今不图。恐后无人解。乞敕下礼部。亟开馆局。首将庞迪我等所有历法。译出成书。崇祯二年五官夏官正弋丰年等。奏举李之藻,西洋人龙化民,邓玉函。同襄历事报可。三年徵西洋陪臣汤若望。又徵西洋陪臣罗雅谷。供事历局。盖中国历法。至元太史郭守敬最号精通。比诸西洋之书。未或测其皮肤。故及西洋之书出。而推算之术。几于大成矣。夫圣莫圣于放勋。而其于授时别立宾饯之官。随时测候。然后方有允釐之效。非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8H 页
 智之有所未周。殆人文肇刱。法制未备。尚容有后出之愈工。若今之历所谓坐致千岁之日至者也。自容成以后几千万年。犹不免有憾。赖西士晓以启之。遂得十分地头。岂非此道之明。有数存者耶。天问略者。即阳玛诺之条答中士也。其论十二重天。槩乎其至矣。而其言曰宜有全书备论。不复致详。惜乎。其全书之不尽译也。今以李之藻所上十四事看。则列宿之外。别有两重之天。动运不同。其一东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极微。从古不觉。盖之藻之亲受者如此。而其略在于书中也。余昔与历家论。妄谓天圆回转。四时生焉。是必有四时所系之天。今以古今中星之差。验之列宿。天之上又必有一天。为四时之符者也。听者或未契悟。今其言曰有一重东西岁差之天。恰与符合。而但南北之差。中国未曾觉也。恨不能闻其定算如何也。夫西洋之于中土。未之相属。各有皇王君主域内。彼特以救世之意。间关来宾。故官之而不肯拜。惟费大官之廪。即一客卿之位耳。中土君臣。方且沾其剩馥。而尊奉之不暇。然犹见闻局于卑狭。敢为井底语曰陪臣某。岂不为达识之所嗤也。良为秉史笔者惜之。
智之有所未周。殆人文肇刱。法制未备。尚容有后出之愈工。若今之历所谓坐致千岁之日至者也。自容成以后几千万年。犹不免有憾。赖西士晓以启之。遂得十分地头。岂非此道之明。有数存者耶。天问略者。即阳玛诺之条答中士也。其论十二重天。槩乎其至矣。而其言曰宜有全书备论。不复致详。惜乎。其全书之不尽译也。今以李之藻所上十四事看。则列宿之外。别有两重之天。动运不同。其一东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极微。从古不觉。盖之藻之亲受者如此。而其略在于书中也。余昔与历家论。妄谓天圆回转。四时生焉。是必有四时所系之天。今以古今中星之差。验之列宿。天之上又必有一天。为四时之符者也。听者或未契悟。今其言曰有一重东西岁差之天。恰与符合。而但南北之差。中国未曾觉也。恨不能闻其定算如何也。夫西洋之于中土。未之相属。各有皇王君主域内。彼特以救世之意。间关来宾。故官之而不肯拜。惟费大官之廪。即一客卿之位耳。中土君臣。方且沾其剩馥。而尊奉之不暇。然犹见闻局于卑狭。敢为井底语曰陪臣某。岂不为达识之所嗤也。良为秉史笔者惜之。跋历书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8L 页
 治历明时。分至定度。冬夏有至。春秋有分。其间长短分数。宜若适均。而考之今历。自春分至秋分其日多。自秋分至春分其日少。厥故何居。盖自夏至日轨。至冬至日轨。合四十八度。其两间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轨。是为天腹赤道也。验之天象。赤道以北迟而以南疾也。日岂有迟疾。即人目有别也。夫星文在东西。其间疏阔。至中天则密矣。非星文之至中天变疏为密。即人目之不同。故较之于指南图。卯酉时刻促。至午时刻缓。此理极明。南北亦然。自北轨至天腹其实长。自天腹至南轨其实短。今历之以为适均。人目也。非天行也。以愚揣之。二至之间。合一百八十二日强。则折其半九十一日强日轨者。是天腹也。虽疑于北狭而南阔。固无伤也。不知历家必以人目排断。果何意哉。若但如此。二至之外。二十二气。恐皆违舛。犹曰一一符合则又不晓其何由耳。然夏至之轨。犹未至于嵩高。而星文皆在日天之上。去日甚远也。人斜以望日。以星文为识。则春秋分日轨所丽之星文。尤非天腹之赤道。以中国万里之地验之。同时候测。星度必别。此又不可不知。
治历明时。分至定度。冬夏有至。春秋有分。其间长短分数。宜若适均。而考之今历。自春分至秋分其日多。自秋分至春分其日少。厥故何居。盖自夏至日轨。至冬至日轨。合四十八度。其两间二十四度。为春秋分之日轨。是为天腹赤道也。验之天象。赤道以北迟而以南疾也。日岂有迟疾。即人目有别也。夫星文在东西。其间疏阔。至中天则密矣。非星文之至中天变疏为密。即人目之不同。故较之于指南图。卯酉时刻促。至午时刻缓。此理极明。南北亦然。自北轨至天腹其实长。自天腹至南轨其实短。今历之以为适均。人目也。非天行也。以愚揣之。二至之间。合一百八十二日强。则折其半九十一日强日轨者。是天腹也。虽疑于北狭而南阔。固无伤也。不知历家必以人目排断。果何意哉。若但如此。二至之外。二十二气。恐皆违舛。犹曰一一符合则又不晓其何由耳。然夏至之轨。犹未至于嵩高。而星文皆在日天之上。去日甚远也。人斜以望日。以星文为识。则春秋分日轨所丽之星文。尤非天腹之赤道。以中国万里之地验之。同时候测。星度必别。此又不可不知。欹器帖跋
物之古莫如欹器。自三五之世。传至鲁庙。孔子说其义。说寄于文而器亡。文虽存。无人把玩。则又惧夫说之俱亡。眉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9H 页
 叟许先生以篆字写而遗后。传至余可宝。愿献之国。藏诸西序。用替大训弘璧。
叟许先生以篆字写而遗后。传至余可宝。愿献之国。藏诸西序。用替大训弘璧。书李相国集
李相国奎报诗云我家本仙枝。又云同是伯阳千载后。愿扶仙李庇馀阴。又云仙李林中作附枝。盖以玄元为祖者。惟唐人是也。虽有后世之讥议。在唐不讳。故相国诗亦据而云然也。凡中国之姓李而源异者。不啻多矣。唯唐与赵郡之外。或多有赐姓及不详来历也。相国距唐止数百馀年。去古未远。必有徵信。而判谓之仙李。则其为与唐同姓定矣。又其赠李姓者曰我李罗天下。君侯表陇西。其所谓我李者。必不泛指源异之诸族。而罗列于天下。惟陇西之望也。唐之李。本陇西成纪人。与汉李广同源也。在我邦则相国既是骊州之李。而与我同姓。我李者亦恐不是国中之姓。其先或从中华移居。始贯于骊州也。先祖少陵公之赴燕。赠草河李姓人诗云与君俱是陇西人。亦与相国诗意同。又未知别有据也耶。姑识所见。以待更考。
跋桐溪集
桐溪甲寅疏云郑造,尹认,丁好宽首发废母杀弟之论。至丁巳废议之成。丁分明有立异文字。则桐溪之议。盖以废母属之造认。以杀弟属之丁也。乌可指立异者为首发乎。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19L 页
 后赵龙洲作汉阴碑云。乞狗舐糠。必欲及米。郑造,尹认,丁好宽讼共发废母。赵公之意。谓杀弟便是废母张本。舍事而诛心曰彼舐糠之狗。意在及米。毕竟同一圈套云尔。至眉叟许相撰桐溪行状。特书曰郑造,尹认,丁好宽首发废母之论。是则元非事实也。盖君子处世。择义未精。鲜免于坠坑落堑。当时杀弟之论起。以张魏公铁塔椎杀皇子㽕事为据。其言亦似有考。然此出小说。不足信也。假饶有之。襁褓索乳之儿。果何罪过。而魏公忍为此耶。高宗无佗子。国脉在是。岂有任其杀之而不禁也耶。若然朱温之欲杀德王裕为正义。而昭宗之不听者悖矣。而况当时之事。其意欲不但在永昌死。而废议遂不可复遏。其操持𣠽柄者闪弄主张。而一时士大夫转辗失脚者多矣。后虽有明言正论。执笔者不许相掩。君子于是乎知所审几而精择焉。
后赵龙洲作汉阴碑云。乞狗舐糠。必欲及米。郑造,尹认,丁好宽讼共发废母。赵公之意。谓杀弟便是废母张本。舍事而诛心曰彼舐糠之狗。意在及米。毕竟同一圈套云尔。至眉叟许相撰桐溪行状。特书曰郑造,尹认,丁好宽首发废母之论。是则元非事实也。盖君子处世。择义未精。鲜免于坠坑落堑。当时杀弟之论起。以张魏公铁塔椎杀皇子㽕事为据。其言亦似有考。然此出小说。不足信也。假饶有之。襁褓索乳之儿。果何罪过。而魏公忍为此耶。高宗无佗子。国脉在是。岂有任其杀之而不禁也耶。若然朱温之欲杀德王裕为正义。而昭宗之不听者悖矣。而况当时之事。其意欲不但在永昌死。而废议遂不可复遏。其操持𣠽柄者闪弄主张。而一时士大夫转辗失脚者多矣。后虽有明言正论。执笔者不许相掩。君子于是乎知所审几而精择焉。玉川遗稿跋
玉川安先生。秩秩礼家。郑寒冈之端友也。寒冈之宰昌宁。建八里书堂。邀为师长。既又铭玉川亭曰手执朱书。头戴程冠。其人如玉。尝望玉川峰屹立亭亭。马上长揖曰如见其人。瀷夙仰寒冈之景行。得其言为重。故敬书卷端。
书逊斋集后
余于诗律家薮多不晓。非人之短余。余实自道。非但自道。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0H 页
 恐古今人未必尽晓何也。如指山而问则高下不可易。指水而问则清浊不可易也。后世之诗则不然。其是与非。未可知也。诗莫尚于李杜。当时韩退之之仰望而不可企及。至欧阳永叔。却云韩胜于杜。若李者。永叔犹不敢云尔。王介甫不独进韩于李。又进欧于韩。以李杜韩之地位。欧王之鉴裁。乖反至此。若是者果可谓有定论乎。吾先大夫业于诗。有集若干卷。刊正之役。托于松谷李词伯。松谷没。托于鸠庵蔡词伯。鸠庵没。托于药山吴词伯。此三公专场主盟。举一世莫敢颉颃之者。其取与舍不同。青红错点。不知适从。于是余不以不晓为耻。乃反致疑于世之自谓辨别如黑白者也。而敢下手于作者之用意乎。余与赵主簿仲裕氏交。但悦其如金如玉。自在于名教中乐地。未见其诗。今其家携遗卷见示。槩禁绝眩耀叱骂之习。有雍容廊庙意思。宛然若复见其人也。昔家兄玉洞公为余道仲裕之诗可与吴幼清对垒。不害为勍敌。余未敢忘也。幼清即松谷词伯之亟许。或求其删。词伯曰尽传。意仲裕乃幼清等辈人。今与其昧昧而妄加甄别。曷若尽传而待目之有珠。如松谷之意也。至其序记祭诔诸篇。其意岂悌。其语反覆。比如车循轨马不覂驾。六辔如柔。旗纛閒閒。终日驰而不见劳勚。余所爱好也。遂书此卷末而还之。
恐古今人未必尽晓何也。如指山而问则高下不可易。指水而问则清浊不可易也。后世之诗则不然。其是与非。未可知也。诗莫尚于李杜。当时韩退之之仰望而不可企及。至欧阳永叔。却云韩胜于杜。若李者。永叔犹不敢云尔。王介甫不独进韩于李。又进欧于韩。以李杜韩之地位。欧王之鉴裁。乖反至此。若是者果可谓有定论乎。吾先大夫业于诗。有集若干卷。刊正之役。托于松谷李词伯。松谷没。托于鸠庵蔡词伯。鸠庵没。托于药山吴词伯。此三公专场主盟。举一世莫敢颉颃之者。其取与舍不同。青红错点。不知适从。于是余不以不晓为耻。乃反致疑于世之自谓辨别如黑白者也。而敢下手于作者之用意乎。余与赵主簿仲裕氏交。但悦其如金如玉。自在于名教中乐地。未见其诗。今其家携遗卷见示。槩禁绝眩耀叱骂之习。有雍容廊庙意思。宛然若复见其人也。昔家兄玉洞公为余道仲裕之诗可与吴幼清对垒。不害为勍敌。余未敢忘也。幼清即松谷词伯之亟许。或求其删。词伯曰尽传。意仲裕乃幼清等辈人。今与其昧昧而妄加甄别。曷若尽传而待目之有珠。如松谷之意也。至其序记祭诔诸篇。其意岂悌。其语反覆。比如车循轨马不覂驾。六辔如柔。旗纛閒閒。终日驰而不见劳勚。余所爱好也。遂书此卷末而还之。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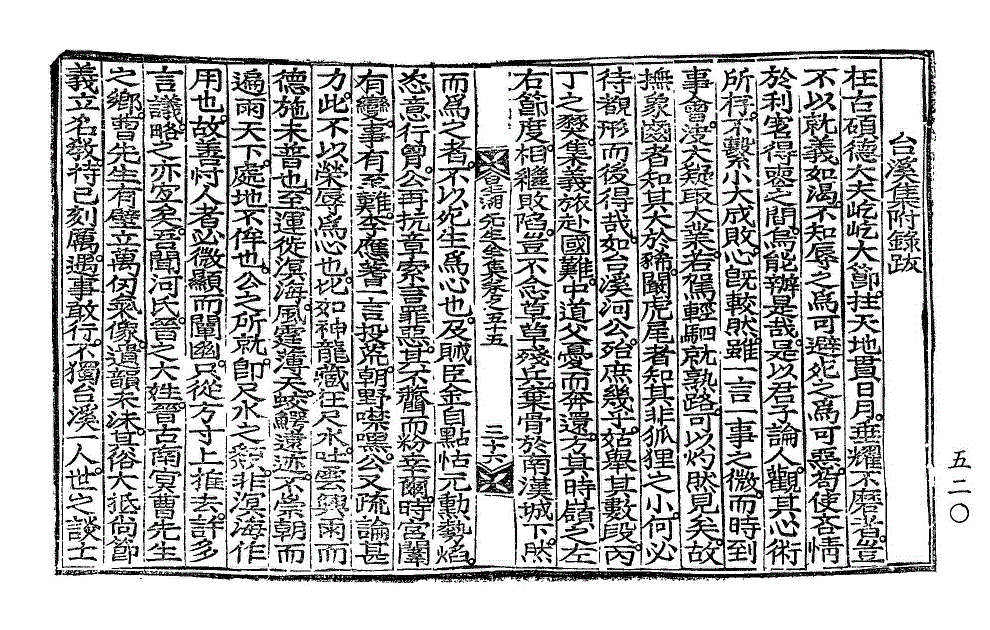 台溪集附录跋
台溪集附录跋在古硕德大夫屹屹大节。拄天地贯日月。垂耀不磨者。岂不以就义如渴。不知辱之为可避死之为可恶。苟使吝情于利害得丧之间。乌能办是哉。是以君子论人。观其心术所存。不系小大成败。心既较然。虽一言一事之微。而时到事会。决大疑取大业。若驾轻驷就熟路。可以灼然见矣。故抚象齿者知其大于豨。阚虎尾者知其非狐狸之小。何必待睹形而后得哉。如台溪河公。殆庶几乎。姑举其数段。丙丁之燹。集义旅赴国难。中道父忧而奔还。方其时岭之左右节度。相继败陷。岂不念草草残兵。弃骨于南汉城下。然而为之者。不以死生为心也。及贼臣金自点怙元勋势焰。恣意行胸。公再抗章索言罪恶。其不齑而粉幸尔。时宫闱有变。事有至难。李应蓍一言投荒。朝野噤嘿。公又疏论甚力。此不以荣辱为心也。比如神龙藏在尺水。吐云兴雨而德施未普也。至运徙溟海。风霆薄天。蛟鳄远迹。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处地不侔也。公之所就。即尺水之类。非溟海作用也。故善忖人者必微显而阐幽。只从方寸上推去。许多言议。略之亦宜矣。吾闻河氏。晋之大姓。晋古南冥曹先生之乡。曹先生有壁立万仞气像。遗韵未沫。其俗大抵尚节义立名教。持己刻厉。遇事敢行。不独台溪一人。世之谈士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1H 页
 大夫高风峻节。必曰晋之河。异时不幸国事有进于是者。其必赖焉。此又原始而要其终。今公之玄孙大观氏。寄示遗稿附录。求一语。敬题卷端。
大夫高风峻节。必曰晋之河。异时不幸国事有进于是者。其必赖焉。此又原始而要其终。今公之玄孙大观氏。寄示遗稿附录。求一语。敬题卷端。盘岩集跋
记昔余年少。在当世文章伯座。听其谈诗曰凡务出奇诡惊动人者。必内存不足也。余得此而寻思。诗即言之成文。贵乎旨远而辞婉。若先有心于眩彩增巧。震耀耳目。则奚啻不得为善言。是以诗莫尚于盛唐。其言多沨沨自在。淡泊而不见痕罅。至其衰季。喜作激越掀撼。凹凸亦间之。不觉声气之愤怒。牛怪蛇神。得罪于黄钟雅音也。余素不晓律家三昧。与人言。但道昔之所闻而已。余所习有晚峰朴大夫者。顿顿诗薮也。耆耋而犹日哦不休。意者是好之笃而觉之深。必不以齿牙之馀。轻许人也。其盘岩集序云天然自成。不烦粉饰。比诸松籁琴韵。余未及阅卷。已信此集之得之有本。而非随俗轩轾。既留之床案。反覆三回。卒无间于朴大夫之言。何赘焉。于是乎敬题其后。
诞隐稿跋
人每患声闻过情。盖十焉八九。此不独群言之易溢。亦其人与有过矣。其或蹈分铲彩。有其实而无其闻。乃所谓君子。昔者吾友李上舍诞隐翁殆近之也。余有憃女。嫁翁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1L 页
 弟之子为妇。熟其内行。为余道其友于弟。无一息之或忘。慈其弟之子与其妻。若己出也。余子孟休尝从妹婿宿外廊。谛听读书声。皆古经文。背诵首尾若水流丸走。夜深不废。时翁已耄老矣。吾闻此二端。佗皆可推也。翁性静不喜交游。惟与一弟块处幽嘿晏晏如也。咫尺门墙之外。无毁亦无誉。苟非昏姻兄弟。固不得以窥其际。夫好名常情也。悠悠齿牙之论。亦必从其求而集。何异蚁蚋之膻酸。于此益知翁之自守真有诚心在也。及其殁。其弟之子存诚以遗集来示。其为诗若文。务去浮华。不侈然以为饰。而笔势有力。斤两自露。往往可诵。吾闻酿大春者。积日月而方成。味久不变。阅寒暑而尚有馀烈。文艺亦然。翁之先祖芝峰子文章擅一时。历数世至悔轩学士。趾美不替。翁又承家守绪。见闻达而气韵不低。岂非有自而来也欤。余一见知其平生所存。有以及之。不徒以一艺观。于是乎书。
弟之子为妇。熟其内行。为余道其友于弟。无一息之或忘。慈其弟之子与其妻。若己出也。余子孟休尝从妹婿宿外廊。谛听读书声。皆古经文。背诵首尾若水流丸走。夜深不废。时翁已耄老矣。吾闻此二端。佗皆可推也。翁性静不喜交游。惟与一弟块处幽嘿晏晏如也。咫尺门墙之外。无毁亦无誉。苟非昏姻兄弟。固不得以窥其际。夫好名常情也。悠悠齿牙之论。亦必从其求而集。何异蚁蚋之膻酸。于此益知翁之自守真有诚心在也。及其殁。其弟之子存诚以遗集来示。其为诗若文。务去浮华。不侈然以为饰。而笔势有力。斤两自露。往往可诵。吾闻酿大春者。积日月而方成。味久不变。阅寒暑而尚有馀烈。文艺亦然。翁之先祖芝峰子文章擅一时。历数世至悔轩学士。趾美不替。翁又承家守绪。见闻达而气韵不低。岂非有自而来也欤。余一见知其平生所存。有以及之。不徒以一艺观。于是乎书。淮海诗稿跋
瀷昔从边公峻卿氏游。峻卿氏之与我友也。非龌龊当世情也。瀷亦曾一过杨之白岩庄。其从子某芳年在侍。盖一见心赏之。今阅三十年而犹一日。说久要津津。其言曰人之相与贵在心。心苟不沫。不系乎倾盖而邂逅。分袂以阔远。余以三十年心为心也。于是寄书累牍。礼卑意溢。不啻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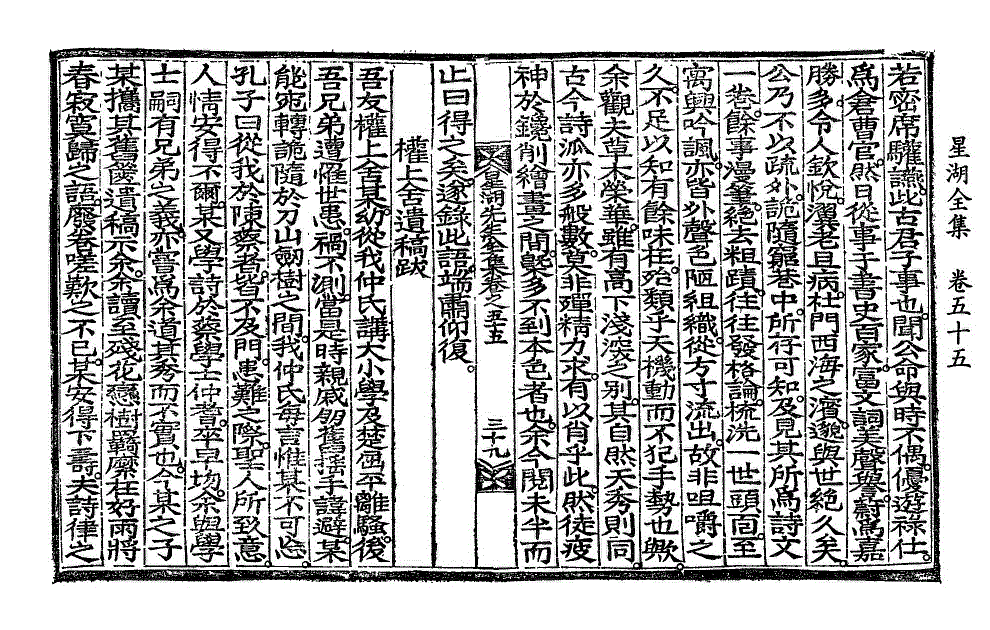 若密席驩宴。此古君子事也。闻公命与时不偶。优游禄仕。为仓曹官。然日从事于书史百家。富文词美声誉。蔚为嘉胜多。令人钦悦。瀷老且病。杜门西海之滨。邈与世绝久矣。公乃不以疏外。诡随穷巷中。所存可知。及见其所为诗文一卷。馀事漫笔。绝去粗迹。往往发格论。梳洗一世头面。至寓兴吟讽。亦皆外声色陋组织。从方寸流出。故非咀嚼之久。不足以知有馀味在。殆类乎天机动而不犯手势也欤。余观夫草木荣华。虽有高下浅深之别。其自然天秀则同。古今诗泒亦多般数。莫非殚精力求。有以肖乎此。然徒疲神于镵削绘画之间。槩多不到本色者也。余今阅未半而止曰得之矣。遂录此语。端肃仰复。
若密席驩宴。此古君子事也。闻公命与时不偶。优游禄仕。为仓曹官。然日从事于书史百家。富文词美声誉。蔚为嘉胜多。令人钦悦。瀷老且病。杜门西海之滨。邈与世绝久矣。公乃不以疏外。诡随穷巷中。所存可知。及见其所为诗文一卷。馀事漫笔。绝去粗迹。往往发格论。梳洗一世头面。至寓兴吟讽。亦皆外声色陋组织。从方寸流出。故非咀嚼之久。不足以知有馀味在。殆类乎天机动而不犯手势也欤。余观夫草木荣华。虽有高下浅深之别。其自然天秀则同。古今诗泒亦多般数。莫非殚精力求。有以肖乎此。然徒疲神于镵削绘画之间。槩多不到本色者也。余今阅未半而止曰得之矣。遂录此语。端肃仰复。权上舍遗稿跋
吾友权上舍某。幼从我仲氏讲大小学及楚屈平离骚。后吾兄弟遭罹世患。祸不测。当是时亲戚朋旧摇手讳避。某能宛转诡随于刀山剑树之间。我仲氏每言惟某不可忘。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患难之际。圣人所致意。人情安得不尔。某又学诗于蔡学士仲耆。卒早殁。余与学士嗣有兄弟之义。亦尝为余道其秀而不实也。今某之子某携其旧箧遗稿示余。余读至残花恋树羁縻在好雨将春寂寞归之语。废卷嗟叹之不已。某安得下寿。夫诗律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2L 页
 兴久矣。沿袭织组。多以似眩真。工与拙或几混矣。独其情到境逼。流出于胃肾者。未可以青黄诬也。如此诗。凄而切。婉而多感。殆其自挽也哉。余头白后死。抚事怀昔。举一联而包其馀。用弁卷首。恨不得更与仲耆学士论此意。
兴久矣。沿袭织组。多以似眩真。工与拙或几混矣。独其情到境逼。流出于胃肾者。未可以青黄诬也。如此诗。凄而切。婉而多感。殆其自挽也哉。余头白后死。抚事怀昔。举一联而包其馀。用弁卷首。恨不得更与仲耆学士论此意。跋尹复春诗卷
复春之与我游二十有馀年。其谈经说礼。娓娓乎馀味。而竿尺频繁。辄发新知。然未尝一及诗律家语。邈然若不自知者。意谓心有所好则功有所专。是必急于此而有未暇焉。及其殁也。余亟吊而索其遗草于其兄某。云亡弟自言学未造而立言妄也。吾实耻之。至若五七言长短篇。有漫兴随录若干卷也。于是益叹斯人之不乐于小成。而迹湮心泯。尚幸咳唾之有馀珠在也。遂携归置房。时一阅过。津津理趣。雅非寒措大口吻。其古体长句。往往披沙玉出。虽瑜不掩瑕。而小瑊大玏。不害为昆崙之抵鹊。吾知复春非用力于此者。自是性敏。信手而得之。使其留心于操觚伎俩。何患不至于滚滚大手堕地汗血。必不屑百步千蹄。是则复春不为尔。
书辉祖卷末
辉祖弱龄能诗。几于玄解。余虽不谙律家技俩。听其言娓娓不倦。意谓是不独有其才。必将由用力而得者。苟能移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3H 页
 此功程。留心于法度规矩之内。亦将大可观矣。今投示余所著若干册。自治身治家。以至于山川土俗风谣物产。无不备述。要之日用之不可阙也。余又谓天下之义理无穷。事变益夥。君子慥慥以求之。切切以居之。日有尽而意犹未休也。若曰吾事已足则便不是道理。苟使因其所已造。益求乎其极焉则其进岂可量哉。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惟辉祖以此勉之。
此功程。留心于法度规矩之内。亦将大可观矣。今投示余所著若干册。自治身治家。以至于山川土俗风谣物产。无不备述。要之日用之不可阙也。余又谓天下之义理无穷。事变益夥。君子慥慥以求之。切切以居之。日有尽而意犹未休也。若曰吾事已足则便不是道理。苟使因其所已造。益求乎其极焉则其进岂可量哉。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惟辉祖以此勉之。跋克己遗卷
克己学于余者也。其王父郡守公。与同高祖兄弟。自郡守公至克己。三世比邻。袒免之义虽杀。而亲与之情尤笃也。人也静而不杂。有雅饬君子风。始读书了了解意。弱冠而能为歌诗。五七言长短篇。稍稍到佳境。卒早夭。人莫不惜之。既而索其遗卷而览之。盖始末咸蓄。纯驳间之。然其至者不烦绳削。已逼造大方鸿匠。比如贵游子弟。年在幼妙。气像云为之际。往往疏脱。而亦能大开口说廊庙语。无可改评。可喜也已。于是略加简别。使其遗孤录之。仍书其端。
跋重哀篇
余家有贤大夫曰白峰子。白峰子没。侧室有二子。伯曰善休。季曰启休。二子早孤。稍知读书。喜左氏内外传。既有得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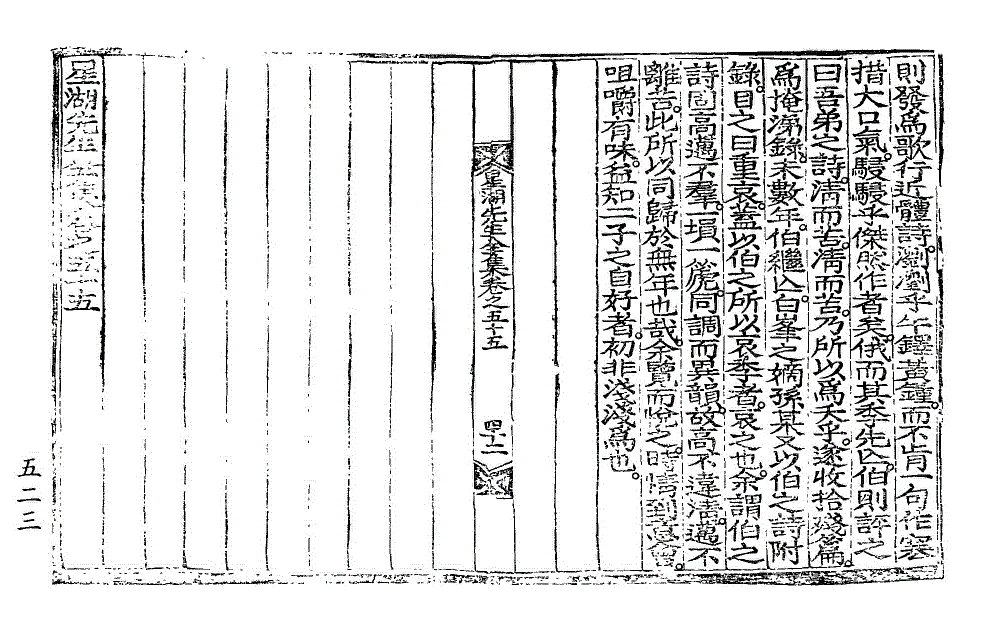 则发为歌行近体诗。浏浏乎牛铎黄钟。而不肯一句作寒措大口气。骎骎乎杰然作者矣。俄而其季先亡。伯则评之曰吾弟之诗。清而苦。清而苦。乃所以为夭乎。遂收拾残篇。为掩涕录。未数年。伯继亡。白峰之嫡孙某又以伯之诗附录。目之曰重哀。盖以伯之所以哀季者。哀之也。余谓伯之诗固高迈不群。一埙一篪。同调而异韵。故高不违清。迈不离苦。此所以同归于无年也哉。余览而悦之。时情到意会。咀嚼有味。益知二子之自好者。初非浅浅为也。
则发为歌行近体诗。浏浏乎牛铎黄钟。而不肯一句作寒措大口气。骎骎乎杰然作者矣。俄而其季先亡。伯则评之曰吾弟之诗。清而苦。清而苦。乃所以为夭乎。遂收拾残篇。为掩涕录。未数年。伯继亡。白峰之嫡孙某又以伯之诗附录。目之曰重哀。盖以伯之所以哀季者。哀之也。余谓伯之诗固高迈不群。一埙一篪。同调而异韵。故高不违清。迈不离苦。此所以同归于无年也哉。余览而悦之。时情到意会。咀嚼有味。益知二子之自好者。初非浅浅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