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x 页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题跋
跋诗传
按鲁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自郐以下无讥焉。注郐第十三曹第十四。季子闻此二国歌。不复讥论之。以其微也。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丁巳才八岁。是时诗之编数。与今见在者无加损。史称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始删诗。邵子曰孔子删诗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皆未有考。愚未知所删果何居耶。
跋书传
自古儒者言尚书多不传。愚以为不然。孔安国之言曰孔子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之文凡百篇。然则在孔子以前者不特百篇。而又失于秦火。今之存仅半耳。诗三百。本无散失。而其逸诗之杂见者不可胜记。况书既删于孔子。又失于秦火。其逸书之见。疑若多于诗也。然自春秋以下至战国间许多人文字。论说书中之言者何限。其见存若干篇外。略不见有一句话杂出于传记何哉。孔安国又曰孔壁科斗书出。以所闻于伏生者。考论文义。增多并序凡五十九篇。其馀错乱磨
题跋
跋诗传
按鲁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自郐以下无讥焉。注郐第十三曹第十四。季子闻此二国歌。不复讥论之。以其微也。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丁巳才八岁。是时诗之编数。与今见在者无加损。史称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始删诗。邵子曰孔子删诗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皆未有考。愚未知所删果何居耶。
跋书传
自古儒者言尚书多不传。愚以为不然。孔安国之言曰孔子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之文凡百篇。然则在孔子以前者不特百篇。而又失于秦火。今之存仅半耳。诗三百。本无散失。而其逸诗之杂见者不可胜记。况书既删于孔子。又失于秦火。其逸书之见。疑若多于诗也。然自春秋以下至战国间许多人文字。论说书中之言者何限。其见存若干篇外。略不见有一句话杂出于传记何哉。孔安国又曰孔壁科斗书出。以所闻于伏生者。考论文义。增多并序凡五十九篇。其馀错乱磨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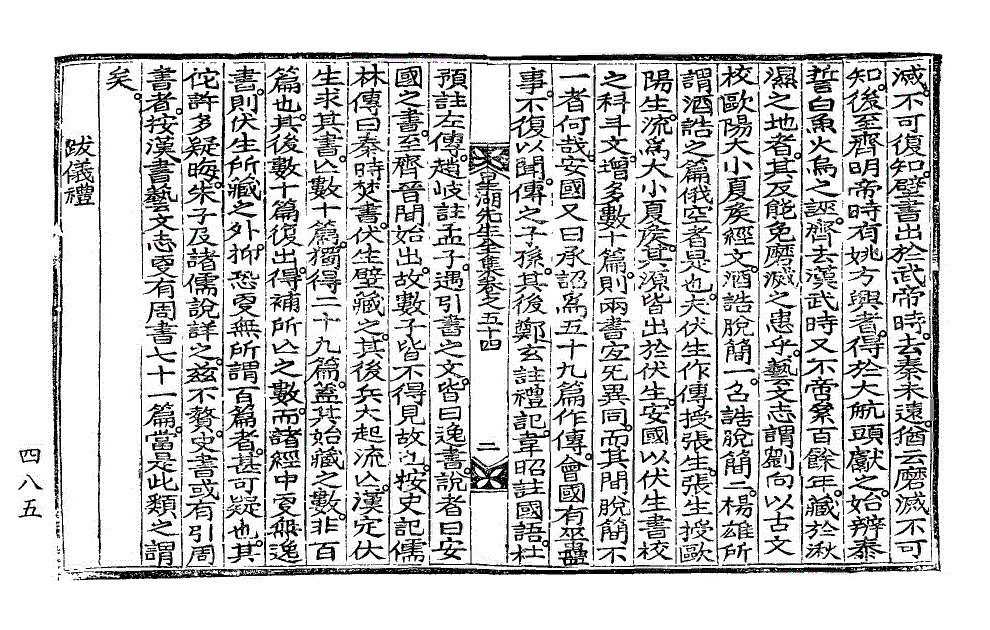 灭。不可复知。壁书出于武帝时。去秦未远。犹云磨灭不可知。后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于大航头献之。始辨泰誓白鱼火乌之诬。齐去汉武时又不啻累百馀年。藏于湫湿之地者。其反能免磨灭之患乎。艺文志谓刘向以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杨雄所谓酒诰之篇俄空者是也。夫伏生作传授张生。张生授欧阳生。流为大小夏侯。其源皆出于伏生。安国以伏生书校之科斗文。增多数十篇。则两书宜无异同。而其间脱简不一者何哉。安国又曰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传之子孙。其后郑玄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赵岐注孟子。遇引书之文。皆曰逸书。说者曰安国之书。至齐晋间始出。故数子皆不得见故也。按史记儒林传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盖其始藏之数。非百篇也。其后数十篇复出。得补所亡之数。而诸经中更无逸书。则伏生所藏之外。抑恐更无所谓百篇者。甚可疑也。其佗许多疑晦。朱子及诸儒说详之。玆不赘。史书或有引周书者。按汉书艺文志更有周书七十一篇。当是此类之谓矣。
灭。不可复知。壁书出于武帝时。去秦未远。犹云磨灭不可知。后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于大航头献之。始辨泰誓白鱼火乌之诬。齐去汉武时又不啻累百馀年。藏于湫湿之地者。其反能免磨灭之患乎。艺文志谓刘向以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杨雄所谓酒诰之篇俄空者是也。夫伏生作传授张生。张生授欧阳生。流为大小夏侯。其源皆出于伏生。安国以伏生书校之科斗文。增多数十篇。则两书宜无异同。而其间脱简不一者何哉。安国又曰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传之子孙。其后郑玄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赵岐注孟子。遇引书之文。皆曰逸书。说者曰安国之书。至齐晋间始出。故数子皆不得见故也。按史记儒林传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盖其始藏之数。非百篇也。其后数十篇复出。得补所亡之数。而诸经中更无逸书。则伏生所藏之外。抑恐更无所谓百篇者。甚可疑也。其佗许多疑晦。朱子及诸儒说详之。玆不赘。史书或有引周书者。按汉书艺文志更有周书七十一篇。当是此类之谓矣。跋仪礼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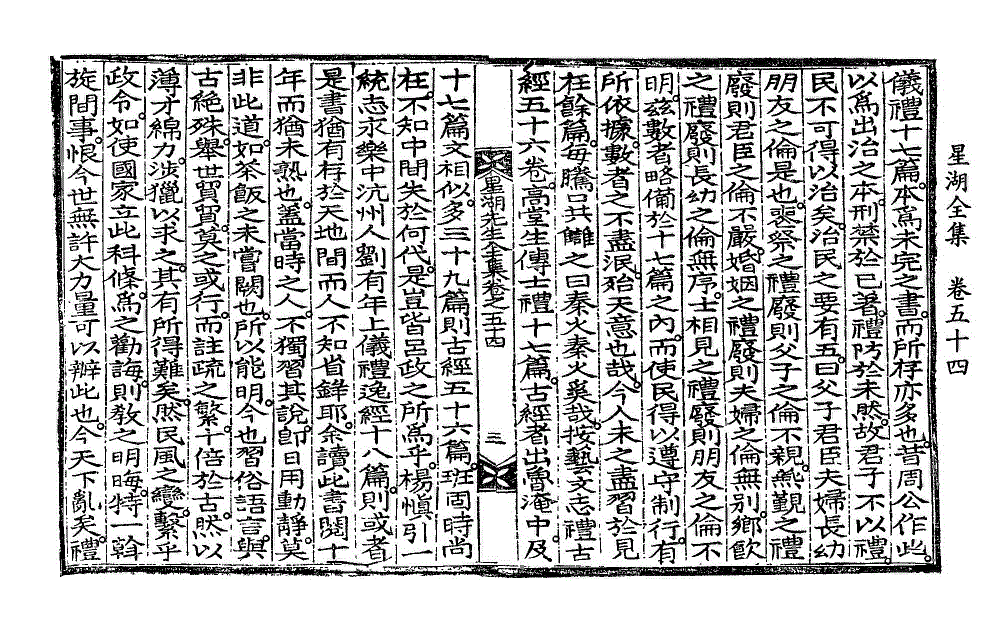 仪礼十七篇。本为未完之书。而所存亦多也。昔周公作此。以为出治之本。刑禁于已著。礼防于未然。故君子不以礼。民不可得以治矣。治民之要有五。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是也。丧祭之礼废则父子之伦不亲。燕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伦不严。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伦无别。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伦无序。士相见之礼废则朋友之伦不明。玆数者略备于十七篇之内。而使民得以遵守制行。有所依据。数者之不尽泯。殆天意也哉。今人未之尽习于见在馀篇。每腾口共雠之曰秦火秦火奚哉。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古经者出鲁淹中。及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则古经五十六篇。班固时尚在。不知中间失于何代。是岂皆吕政之所为乎。杨慎引一统志永乐中沆州人刘有年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或者是书犹有存于天地间而人不知省录耶。余读此书阅十年而犹未熟也。盖当时之人。不独习其说。即日用动静。莫非此道。如茶饭之未尝阙也。所以能明。今也习俗语言。与古绝殊。举世贸贸。莫之或行。而注疏之繁。十倍于古。然以薄才绵力。涉猎以求之。其有所得难矣。然民风之变。系乎政令。如使国家立此科条。为之劝诲。则教之明晦。特一斡旋间事。恨今世无许大力量可以办此也。今天下乱矣。礼
仪礼十七篇。本为未完之书。而所存亦多也。昔周公作此。以为出治之本。刑禁于已著。礼防于未然。故君子不以礼。民不可得以治矣。治民之要有五。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是也。丧祭之礼废则父子之伦不亲。燕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伦不严。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伦无别。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伦无序。士相见之礼废则朋友之伦不明。玆数者略备于十七篇之内。而使民得以遵守制行。有所依据。数者之不尽泯。殆天意也哉。今人未之尽习于见在馀篇。每腾口共雠之曰秦火秦火奚哉。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古经者出鲁淹中。及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则古经五十六篇。班固时尚在。不知中间失于何代。是岂皆吕政之所为乎。杨慎引一统志永乐中沆州人刘有年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或者是书犹有存于天地间而人不知省录耶。余读此书阅十年而犹未熟也。盖当时之人。不独习其说。即日用动静。莫非此道。如茶饭之未尝阙也。所以能明。今也习俗语言。与古绝殊。举世贸贸。莫之或行。而注疏之繁。十倍于古。然以薄才绵力。涉猎以求之。其有所得难矣。然民风之变。系乎政令。如使国家立此科条。为之劝诲。则教之明晦。特一斡旋间事。恨今世无许大力量可以办此也。今天下乱矣。礼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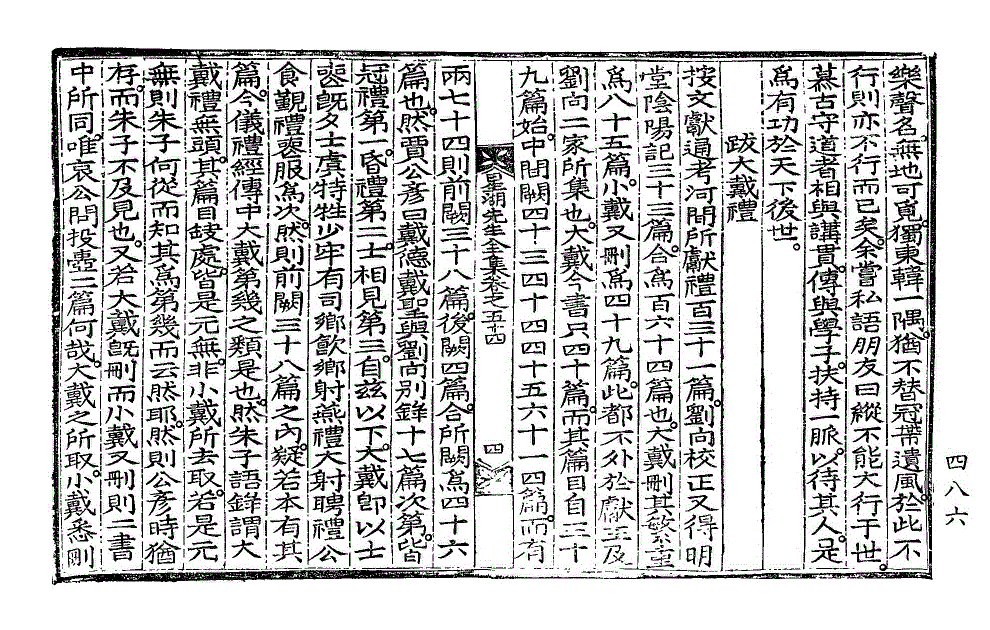 乐声名。无地可觅。独东韩一隅。犹不替冠带遗风。于此不行则亦不行而已矣。余尝私语朋友曰纵不能大行于世。慕古守道者相与讲贯。传与学子。扶持一脉。以待其人。是为有功于天下后世。
乐声名。无地可觅。独东韩一隅。犹不替冠带遗风。于此不行则亦不行而已矣。余尝私语朋友曰纵不能大行于世。慕古守道者相与讲贯。传与学子。扶持一脉。以待其人。是为有功于天下后世。跋大戴礼
按文献通考河间所献礼百三十一篇。刘向校正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合为百六十四篇也。大戴删其繁重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此都不外于献王及刘向二家所集也。大戴今书只四十篇。而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中间阙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而有两七十四则前阙三十八篇。后阙四篇。合所阙为四十六篇也。然贾公彦曰戴德戴圣与刘向别录十七篇次第。皆冠礼第一。昏礼第二。士相见第三。自玆以下。大戴即以士丧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乡饮乡射燕礼大射聘礼公食觐礼丧服为次。然则前阙三十八篇之内。疑若本有其篇。今仪礼经传中大戴第几之类是也。然朱子语录谓大戴礼无头。其篇目缺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若是元无则朱子何从而知其为第几而云然耶。然则公彦时犹存。而朱子不及见也。又若大戴既删而小戴又删则二书中所同。唯哀公问投壶二篇何哉。大戴之所取。小戴悉删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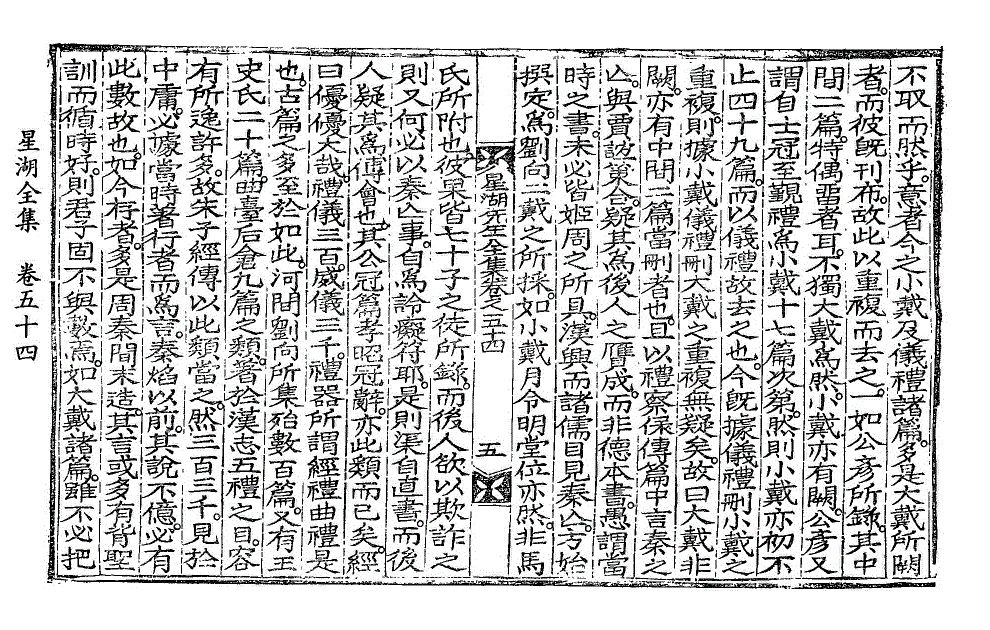 不取而然乎。意者今之小戴及仪礼诸篇。多是大戴所阙者。而彼既刊布。故此以重复而去之。一如公彦所录。其中间二篇。特偶留者耳。不独大戴为然。小戴亦有阙。公彦又谓自士冠至觐礼为小戴十七篇次第。然则小戴亦初不止四十九篇。而以仪礼故去之也。今既据仪礼删小戴之重复。则据小戴仪礼删大戴之重复无疑矣。故曰大戴非阙。亦有中间二篇当删者也。且以礼察保传篇中言秦之亡。与贾谊策合。疑其为后人之赝成。而非德本书。愚谓当时之书。未必皆姬周之所具。汉兴而诸儒目见秦亡。方始撰定。为刘向二戴之所采。如小戴月令明堂位亦然。非马氏所附也。彼果皆七十子之徒所录。而后人欲以欺诈之则又何必以秦亡事。自为詅痴符耶。是则渠自直书。而后人疑其为傅会也。其公冠篇孝昭冠辞。亦此类而已矣。经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所谓经礼曲礼是也。古篇之多至于如此。河间刘向所集殆数百篇。又有王史氏二十篇。曲台后仓九篇之类。著于汉志五礼之目。容有所逸许多。故朱子经传以此类当之。然三百三千。见于中庸。必据当时著行者而为言。秦焰以前。其说不亿。必有此数故也。如今存者。多是周秦间末造。其言或多有背圣训而循时好。则君子固不与数焉。如大戴诸篇。虽不必把
不取而然乎。意者今之小戴及仪礼诸篇。多是大戴所阙者。而彼既刊布。故此以重复而去之。一如公彦所录。其中间二篇。特偶留者耳。不独大戴为然。小戴亦有阙。公彦又谓自士冠至觐礼为小戴十七篇次第。然则小戴亦初不止四十九篇。而以仪礼故去之也。今既据仪礼删小戴之重复。则据小戴仪礼删大戴之重复无疑矣。故曰大戴非阙。亦有中间二篇当删者也。且以礼察保传篇中言秦之亡。与贾谊策合。疑其为后人之赝成。而非德本书。愚谓当时之书。未必皆姬周之所具。汉兴而诸儒目见秦亡。方始撰定。为刘向二戴之所采。如小戴月令明堂位亦然。非马氏所附也。彼果皆七十子之徒所录。而后人欲以欺诈之则又何必以秦亡事。自为詅痴符耶。是则渠自直书。而后人疑其为傅会也。其公冠篇孝昭冠辞。亦此类而已矣。经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所谓经礼曲礼是也。古篇之多至于如此。河间刘向所集殆数百篇。又有王史氏二十篇。曲台后仓九篇之类。著于汉志五礼之目。容有所逸许多。故朱子经传以此类当之。然三百三千。见于中庸。必据当时著行者而为言。秦焰以前。其说不亿。必有此数故也。如今存者。多是周秦间末造。其言或多有背圣训而循时好。则君子固不与数焉。如大戴诸篇。虽不必把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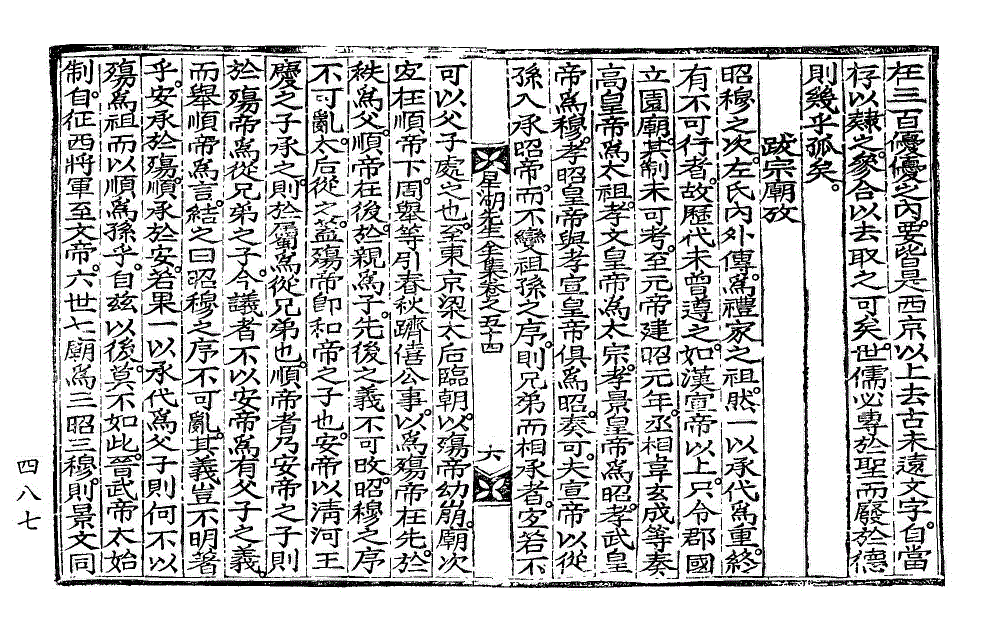 在三百优优之内。要皆是西京以上去古未远文字。自当存以肄之。参合以去取之可矣。世儒必专于圣而废于德则几乎孤矣。
在三百优优之内。要皆是西京以上去古未远文字。自当存以肄之。参合以去取之可矣。世儒必专于圣而废于德则几乎孤矣。跋宗庙考
昭穆之次。左氏内外传。为礼家之祖。然一以承代为重。终有不可行者。故历代未曾遵之。如汉宣帝以上。只令郡国立园庙。其制未可考。至元帝建昭元年。丞相韦玄成等奏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奏可。夫宣帝以从孙入承昭帝。而不变祖孙之序。则兄弟而相承者。宜若不可以父子处之也。至东京梁太后临朝。以殇帝幼崩。庙次宜在顺帝下。周举等引春秋跻僖公事。以为殇帝在先。于秩为父。顺帝在后。于亲为子。先后之义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乱。太后从之。盖殇帝即和帝之子也。安帝以清河王庆之子承之。则于属为从兄弟也。顺帝者乃安帝之子则于殇帝为从兄弟之子。今议者不以安帝为有父子之义。而举顺帝为言。结之曰昭穆之序不可乱。其义岂不明著乎。安承于殇。顺承于安。若果一以承代为父子则何不以殇为祖而以顺为孙乎。自玆以后。莫不如此。晋武帝太始制。自征西将军至文帝。六世七庙为三昭三穆。则景文同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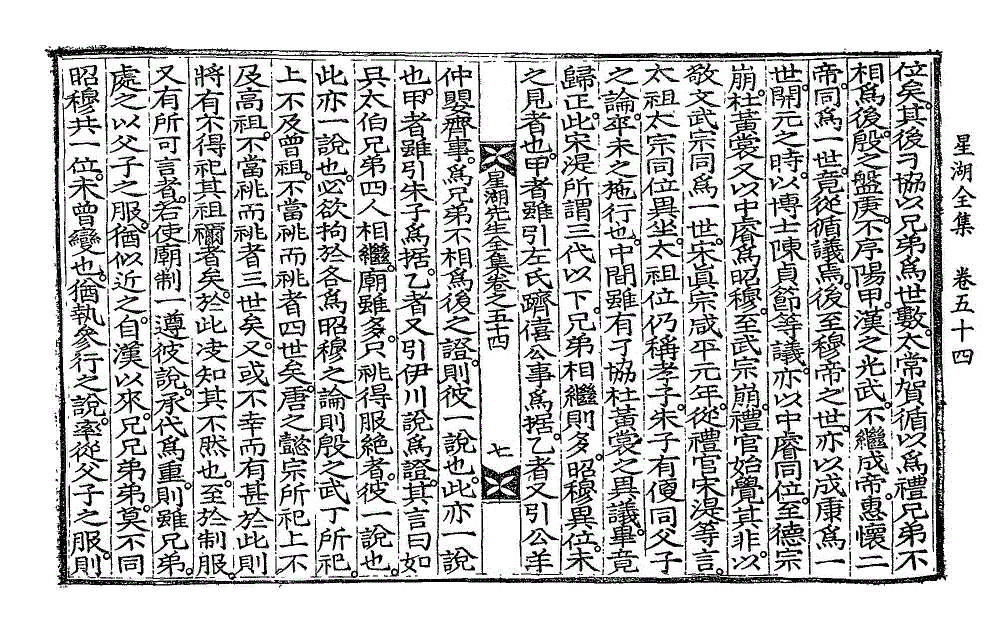 位矣。其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太常贺循以为礼兄弟不相为后。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惠怀二帝。同为一世。竟从循议焉。后至穆帝之世。亦以成康为一世。开元之时。以博士陈贞节等议。亦以中睿同位。至德宗崩。杜黄裳又以中睿为昭穆。至武宗崩。礼官始觉其非。以敬文武宗同为一世。宋真宗咸平元年。从礼官宋湜等言。太祖太宗同位异坐。太祖位仍称孝子。朱子有便同父子之论。卒未之施行也。中间虽有刁协,杜黄裳之异议。毕竟归正。此宋湜所谓三代以下。兄弟相继则多。昭穆异位。未之见者也。甲者虽引左氏跻僖公事为据。乙者又引公羊仲婴齐事。为兄弟不相为后之證。则彼一说也。此亦一说也。甲者虽引朱子为据。乙者又引伊川说为證。其言曰如吴太伯兄弟四人相继。庙虽多。只祧得服绝者。彼一说也。此亦一说也。必欲拘于各为昭穆之论则殷之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不当祧而祧者四世矣。唐之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不当祧而祧者三世矣。又或不幸而有甚于此则将有不得祀其祖祢者矣。于此决知其不然也。至于制服。又有所可言者。若使庙制一遵彼说。承代为重。则虽兄弟。处之以父子之服。犹似近之。自汉以来。兄兄弟弟。莫不同昭穆共一位。未曾变也。犹执参行之说。率从父子之服。则
位矣。其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太常贺循以为礼兄弟不相为后。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惠怀二帝。同为一世。竟从循议焉。后至穆帝之世。亦以成康为一世。开元之时。以博士陈贞节等议。亦以中睿同位。至德宗崩。杜黄裳又以中睿为昭穆。至武宗崩。礼官始觉其非。以敬文武宗同为一世。宋真宗咸平元年。从礼官宋湜等言。太祖太宗同位异坐。太祖位仍称孝子。朱子有便同父子之论。卒未之施行也。中间虽有刁协,杜黄裳之异议。毕竟归正。此宋湜所谓三代以下。兄弟相继则多。昭穆异位。未之见者也。甲者虽引左氏跻僖公事为据。乙者又引公羊仲婴齐事。为兄弟不相为后之證。则彼一说也。此亦一说也。甲者虽引朱子为据。乙者又引伊川说为證。其言曰如吴太伯兄弟四人相继。庙虽多。只祧得服绝者。彼一说也。此亦一说也。必欲拘于各为昭穆之论则殷之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不当祧而祧者四世矣。唐之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不当祧而祧者三世矣。又或不幸而有甚于此则将有不得祀其祖祢者矣。于此决知其不然也。至于制服。又有所可言者。若使庙制一遵彼说。承代为重。则虽兄弟。处之以父子之服。犹似近之。自汉以来。兄兄弟弟。莫不同昭穆共一位。未曾变也。犹执参行之说。率从父子之服。则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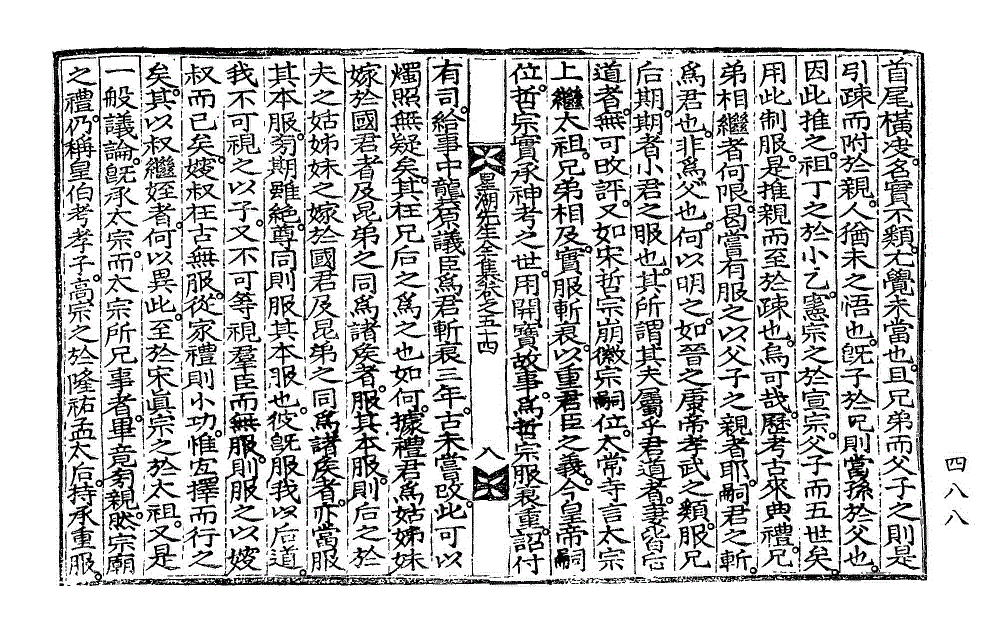 首尾横决。名实不类。尤觉未当也。且兄弟而父子之则是引疏而附于亲。人犹未之悟也。既子于兄则当孙于父也。因此推之。祖丁之于小乙。宪宗之于宣宗。父子而五世矣。用此制服。是推亲而至于疏也。乌可哉。历考古来典礼。兄弟相继者何限。曷尝有服之以父子之亲者耶。嗣君之斩。为君也。非为父也。何以明之。如晋之康帝孝武之类。服兄后期。期者小君之服也。其所谓其夫属乎君道者。妻皆后道者。无可改评。又如宋哲宗崩徽宗嗣位。太常寺言太宗上继太祖。兄弟相及。实服斩衰。以重君臣之义。今皇帝嗣位。哲宗实承神考之世。用开宝故事。为哲宗服衰重。诏付有司。给事中龚原议臣为君斩衰三年。古未尝改。此可以烛照无疑矣。其在兄后之为之也如何。据礼君为姑姊妹嫁于国君者及昆弟之同为诸侯者。服其本服。则后之于夫之姑姊妹之嫁于国君及昆弟之同为诸侯者。亦当服其本服。旁期虽绝。尊同则服其本服也。彼既服我以后道。我不可视之以子。又不可等视群臣而无服。则服之以嫂叔而已矣。嫂叔在古无服。从家礼则小功。惟宜择而行之矣。其以叔继侄者。何以异此。至于宋真宗之于太祖。又是一般议论。既承太宗。而太宗所兄事者。毕竟旁亲。然宗庙之礼。仍称皇伯考孝子。高宗之于隆祐孟太后。持承重服。
首尾横决。名实不类。尤觉未当也。且兄弟而父子之则是引疏而附于亲。人犹未之悟也。既子于兄则当孙于父也。因此推之。祖丁之于小乙。宪宗之于宣宗。父子而五世矣。用此制服。是推亲而至于疏也。乌可哉。历考古来典礼。兄弟相继者何限。曷尝有服之以父子之亲者耶。嗣君之斩。为君也。非为父也。何以明之。如晋之康帝孝武之类。服兄后期。期者小君之服也。其所谓其夫属乎君道者。妻皆后道者。无可改评。又如宋哲宗崩徽宗嗣位。太常寺言太宗上继太祖。兄弟相及。实服斩衰。以重君臣之义。今皇帝嗣位。哲宗实承神考之世。用开宝故事。为哲宗服衰重。诏付有司。给事中龚原议臣为君斩衰三年。古未尝改。此可以烛照无疑矣。其在兄后之为之也如何。据礼君为姑姊妹嫁于国君者及昆弟之同为诸侯者。服其本服。则后之于夫之姑姊妹之嫁于国君及昆弟之同为诸侯者。亦当服其本服。旁期虽绝。尊同则服其本服也。彼既服我以后道。我不可视之以子。又不可等视群臣而无服。则服之以嫂叔而已矣。嫂叔在古无服。从家礼则小功。惟宜择而行之矣。其以叔继侄者。何以异此。至于宋真宗之于太祖。又是一般议论。既承太宗。而太宗所兄事者。毕竟旁亲。然宗庙之礼。仍称皇伯考孝子。高宗之于隆祐孟太后。持承重服。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9H 页
 亦据汉顺帝虽承安帝为之子。又以子道奉殇帝。古事宜然。然则嗣皇之于太后。当持重。而太后之为之也亦服之以子道。外此无佗道矣。
亦据汉顺帝虽承安帝为之子。又以子道奉殇帝。古事宜然。然则嗣皇之于太后。当持重。而太后之为之也亦服之以子道。外此无佗道矣。跋白虎通[二]
典籍渐坏。将无所考信。故于是作白虎议奏。是时传记之存者尚多。据艺文志可见。而如此书所引王度记礼记谥法之类。何可以复见。盖聚天下之书。极人物之选。辨五经同异。不比后世之孤章臆断。则其言殆可以有信矣。近时儒术亦鲜。有蓄此书者茫不知为何语。甚可异耳。然多据纬书与经训比。为世儒之所短。按史汉顺帝时张衡上疏言图谶成于哀平之际。虚伪之徒。要世欺妄。距此书之成才五十有馀年。而是非不相侔如此也。自中兴至书成。亦不过五十年。纬书之出亦不久矣。若只是夏贺良等无忌惮之所为。则宿儒如班固贾逵又何以尊信至此。甚可怪也。今纬书之存者亦多。其诞妄不经。固是可恶。而间或有不可泯者。惟在览而采之。
凡贫士家书籍极难得。唯有缮写可以略备。然笔手又难得。余借人白虎通一帙。使儿辈移录。鍊捣纸稍明滑。加之卷上。使字画透见。然后依墨写过。手虽生。顿整不乱。又免阙落。亦一术也。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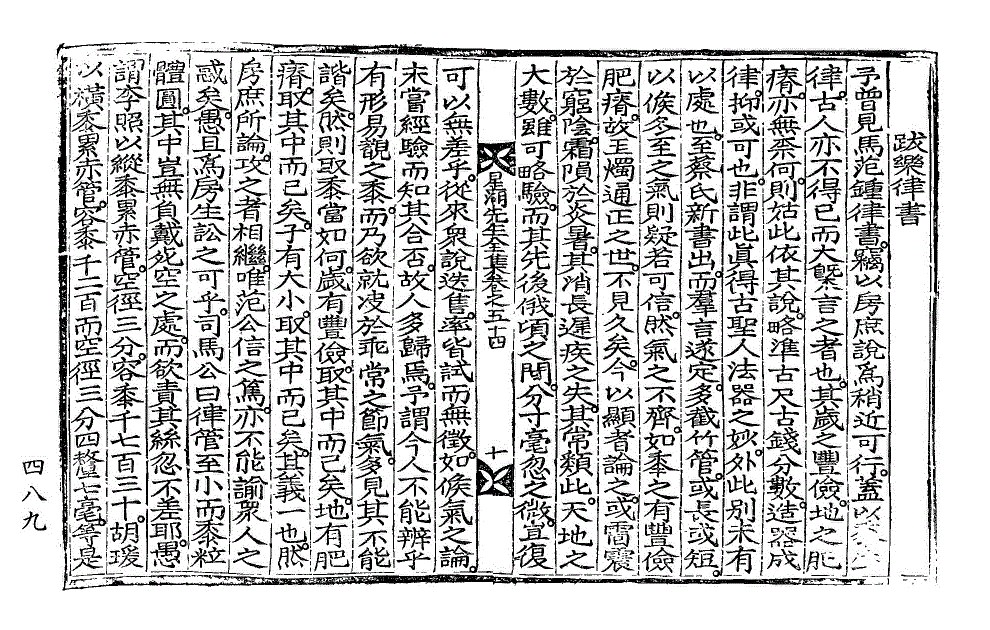 跋乐律书
跋乐律书予曾见马范钟律书。窃以房庶说为稍近可行。盖以黍生律。古人亦不得已而大槩言之者也。其岁之丰俭。地之肥瘠。亦无柰何。则姑此依其说。略准古尺古钱分数。造器成律。抑或可也。非谓此真得古圣人法器之妙。外此别未有以处也。至蔡氏新书出。而群言遂定。多截竹管。或长或短。以候冬至之气则疑若可信。然气之不齐。如黍之有丰俭肥瘠。故玉烛通正之世。不见久矣。今以显者论之。或䨓震于穷阴。霜陨于炎暑。其消长迟疾之失。其常类此。天地之大数。虽可略验。而其先后俄顷之间。分寸毫忽之微。岂复可以无差乎。从来众说迭售。率皆试而无徵。如候气之论。未尝经验而知其合否。故人多归焉。予谓今人不能辨乎有形易睹之黍。而乃欲就决于乖常之节气。多见其不能谐矣。然则取黍当如何。岁有丰俭。取其中而已矣。地有肥瘠。取其中而已矣。子有大小。取其中而已矣。其义一也。然房庶所论。攻之者相继。唯范公信之笃。亦不能谕众人之惑矣。愚且为房生讼之可乎。司马公曰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戴死空之处。而欲责其丝忽不差耶。愚谓李照以纵黍累赤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赤管。容黍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七毫。等是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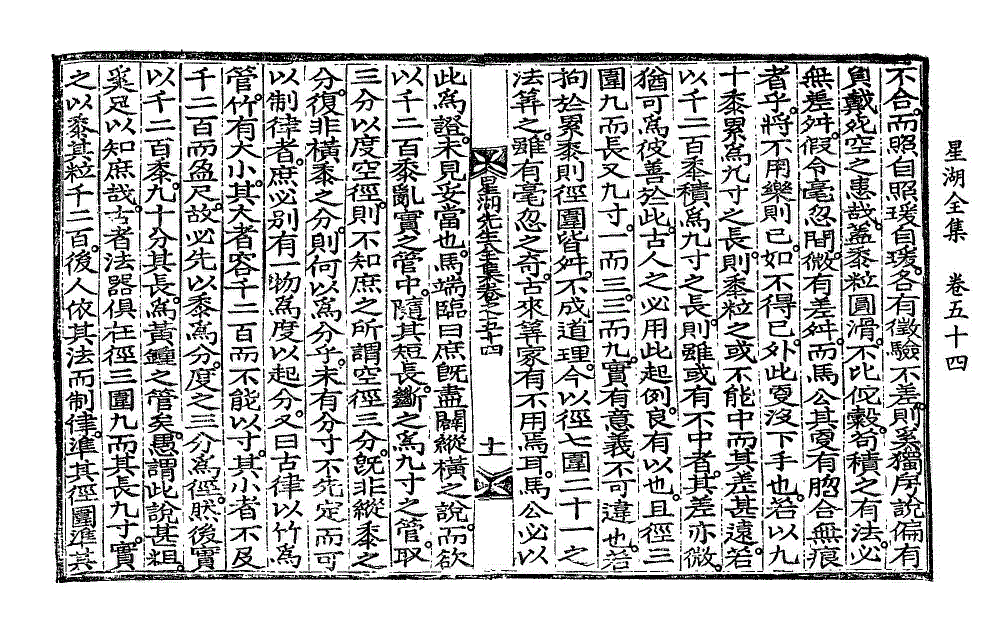 不合。而照自照瑗自瑗。各有徵验不差。则奚独房说偏有负戴死空之患哉。盖黍粒圆滑。不比佗谷。苟积之有法。必无差舛。假令毫忽间。微有差舛。而马公其更有吻合无痕者乎。将不用乐则已。如不得已。外此更没下手也。若以九十黍累为九寸之长。则黍粒之或不能中而其差甚远。若以千二百黍积为九寸之长。则虽或有不中者。其差亦微。犹可为彼善于此。古人之必用此起例。良有以也。且径三围九而长又九寸。一而三。三而九。实有意义不可违也。若拘于累黍则径围皆舛。不成道理。今以径七围二十一之法算之。虽有毫忽之奇。古来算家有不用焉耳。马公必以此为證。未见妥当也。马端临曰庶既尽辟纵横之说。而欲以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既非纵黍之分。复非横黍之分。则何以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庶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又曰古律以竹为管。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而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而盈尺。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然后实以千二百黍。九十分其长。为黄钟之管矣。愚谓此说甚粗。奚足以知庶哉。古者法器俱在径三围九而其长九寸。实之以黍其粒千二百。后人依其法而制律。准其径围准其
不合。而照自照瑗自瑗。各有徵验不差。则奚独房说偏有负戴死空之患哉。盖黍粒圆滑。不比佗谷。苟积之有法。必无差舛。假令毫忽间。微有差舛。而马公其更有吻合无痕者乎。将不用乐则已。如不得已。外此更没下手也。若以九十黍累为九寸之长。则黍粒之或不能中而其差甚远。若以千二百黍积为九寸之长。则虽或有不中者。其差亦微。犹可为彼善于此。古人之必用此起例。良有以也。且径三围九而长又九寸。一而三。三而九。实有意义不可违也。若拘于累黍则径围皆舛。不成道理。今以径七围二十一之法算之。虽有毫忽之奇。古来算家有不用焉耳。马公必以此为證。未见妥当也。马端临曰庶既尽辟纵横之说。而欲以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既非纵黍之分。复非横黍之分。则何以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庶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又曰古律以竹为管。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而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而盈尺。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然后实以千二百黍。九十分其长。为黄钟之管矣。愚谓此说甚粗。奚足以知庶哉。古者法器俱在径三围九而其长九寸。实之以黍其粒千二百。后人依其法而制律。准其径围准其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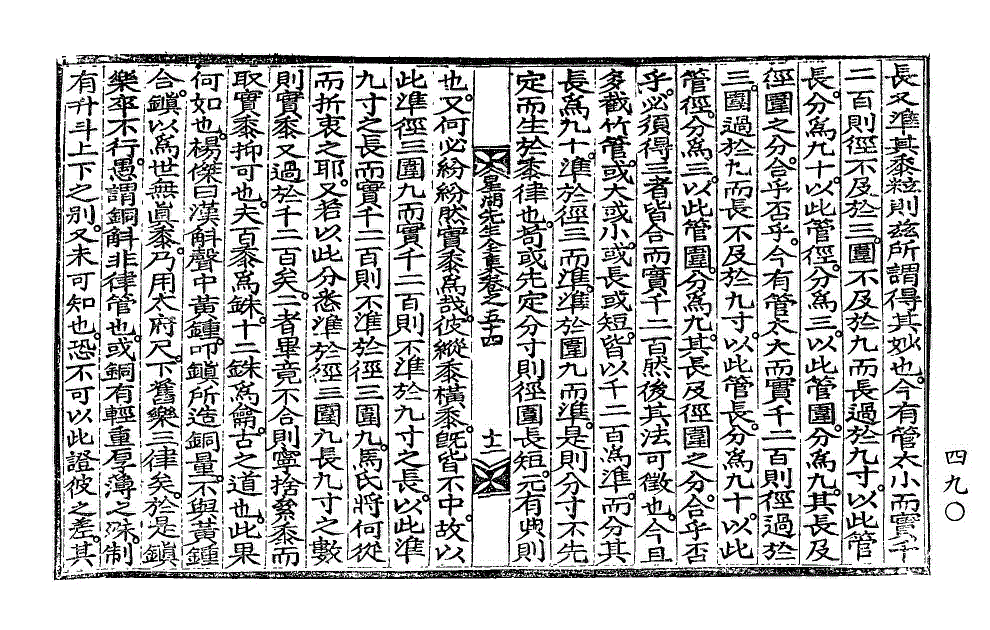 长又准其黍粒则玆所谓得其妙也。今有管太小而实千二百则径不及于三。围不及于九而长过于九寸。以此管长。分为九十。以此管径。分为三。以此管围。分为九。其长及径围之分。合乎否乎。今有管太大而实千二百则径过于三。围过于九而长不及于九寸。以此管长。分为九十。以此管径。分为三。以此管围。分为九。其长及径围之分。合乎否乎。必须得三者皆合而实千二百然后其法可徵也。今且多截竹管。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以千二百为准。而分其长为九十。准于径三而准。准于围九而准。是则分寸不先定而生于黍律也。苟或先定分寸则径围长短。元有典则也。又何必纷纷然实黍为哉。彼纵黍横黍。既皆不中。故以此准径三围九而实千二百则不准于九寸之长。以此准九寸之长而实千二百则不准于径三围九。马氏将何从而折衷之耶。又若以此分悉准于径三围九长九寸之数则实黍又过于千二百矣。二者毕竟不合则宁舍累黍而取实黍抑可也。夫百黍为铢。十二铢为龠。古之道也。此果何如也。杨杰曰汉斛声中黄钟。叩镇所造铜量。不与黄钟合。镇以为世无真黍。乃用太府尺。下旧乐三律矣。于是镇乐卒不行。愚谓铜斛非律管也。或铜有轻重厚薄之殊。制有升斗上下之别。又未可知也。恐不可以此證彼之差。其
长又准其黍粒则玆所谓得其妙也。今有管太小而实千二百则径不及于三。围不及于九而长过于九寸。以此管长。分为九十。以此管径。分为三。以此管围。分为九。其长及径围之分。合乎否乎。今有管太大而实千二百则径过于三。围过于九而长不及于九寸。以此管长。分为九十。以此管径。分为三。以此管围。分为九。其长及径围之分。合乎否乎。必须得三者皆合而实千二百然后其法可徵也。今且多截竹管。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以千二百为准。而分其长为九十。准于径三而准。准于围九而准。是则分寸不先定而生于黍律也。苟或先定分寸则径围长短。元有典则也。又何必纷纷然实黍为哉。彼纵黍横黍。既皆不中。故以此准径三围九而实千二百则不准于九寸之长。以此准九寸之长而实千二百则不准于径三围九。马氏将何从而折衷之耶。又若以此分悉准于径三围九长九寸之数则实黍又过于千二百矣。二者毕竟不合则宁舍累黍而取实黍抑可也。夫百黍为铢。十二铢为龠。古之道也。此果何如也。杨杰曰汉斛声中黄钟。叩镇所造铜量。不与黄钟合。镇以为世无真黍。乃用太府尺。下旧乐三律矣。于是镇乐卒不行。愚谓铜斛非律管也。或铜有轻重厚薄之殊。制有升斗上下之别。又未可知也。恐不可以此證彼之差。其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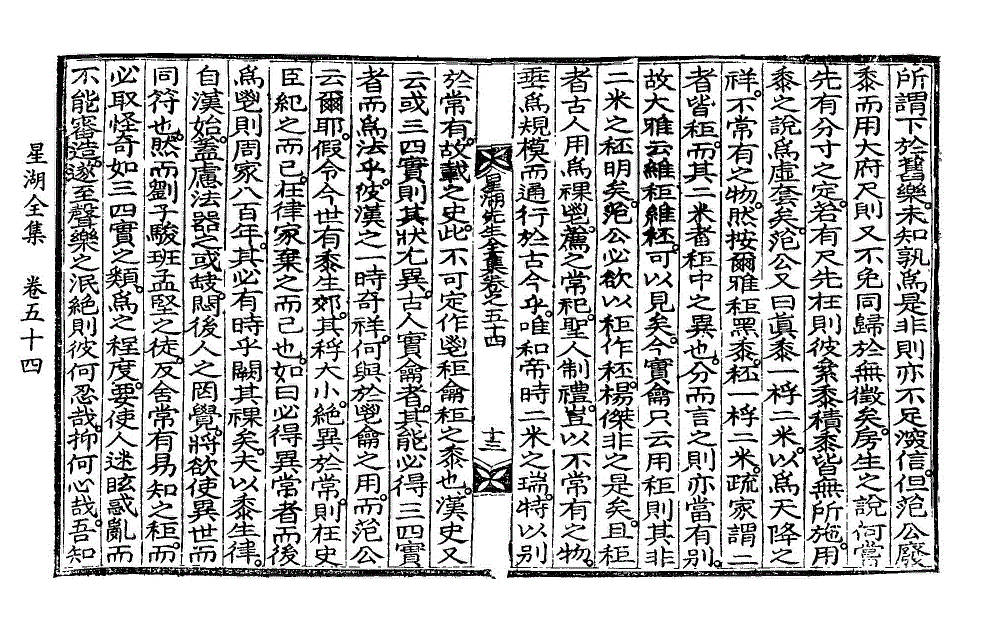 所谓下于旧乐。未知孰为是非则亦不足深信。但范公废黍而用大府尺则又不免同归于无徵矣。房生之说何尝先有分寸之定。若有尺先在则彼累黍积黍皆无所施。用黍之说为虚套矣。范公又曰真黍一桴二米。以为天降之祥。不常有之物。然按尔雅秬黑黍。秠一桴二米。疏家谓二者皆秬。而其二米者秬中之异也。分而言之则亦当有别。故大雅云维秬维秠。可以见矣。今实龠只云用秬则其非二米之秠明矣。范公必欲以秬作秠。杨杰非之是矣。且秬者古人用为祼鬯。荐之常祀。圣人制礼。岂以不常有之物。垂为规模而通行于古今乎。唯和帝时二米之瑞。特以别于常有。故载之史。此不可定作鬯秬龠秬之黍也。汉史又云或三四实则其状尤异。古人实龠者。其能必得三四实者而为法乎。彼汉之一时奇祥。何与于鬯龠之用。而范公云尔耶。假令今世有黍生郊。其稃大小。绝异于常。则在史臣纪之而已。在律家弃之而已也。如曰必得异常者而后为鬯则周家八百年。其必有时乎阙其祼矣。夫以黍生律。自汉始。盖虑法器之或缺。闷后人之罔觉。将欲使异世而同符也。然而刘子骏班孟坚之徒。反舍常有易知之秬。而必取怪奇如三四实之类。为之程度。要使人迷眩惑乱而不能审造。遂至声乐之泯绝则彼何忍哉。抑何心哉。吾知
所谓下于旧乐。未知孰为是非则亦不足深信。但范公废黍而用大府尺则又不免同归于无徵矣。房生之说何尝先有分寸之定。若有尺先在则彼累黍积黍皆无所施。用黍之说为虚套矣。范公又曰真黍一桴二米。以为天降之祥。不常有之物。然按尔雅秬黑黍。秠一桴二米。疏家谓二者皆秬。而其二米者秬中之异也。分而言之则亦当有别。故大雅云维秬维秠。可以见矣。今实龠只云用秬则其非二米之秠明矣。范公必欲以秬作秠。杨杰非之是矣。且秬者古人用为祼鬯。荐之常祀。圣人制礼。岂以不常有之物。垂为规模而通行于古今乎。唯和帝时二米之瑞。特以别于常有。故载之史。此不可定作鬯秬龠秬之黍也。汉史又云或三四实则其状尤异。古人实龠者。其能必得三四实者而为法乎。彼汉之一时奇祥。何与于鬯龠之用。而范公云尔耶。假令今世有黍生郊。其稃大小。绝异于常。则在史臣纪之而已。在律家弃之而已也。如曰必得异常者而后为鬯则周家八百年。其必有时乎阙其祼矣。夫以黍生律。自汉始。盖虑法器之或缺。闷后人之罔觉。将欲使异世而同符也。然而刘子骏班孟坚之徒。反舍常有易知之秬。而必取怪奇如三四实之类。为之程度。要使人迷眩惑乱而不能审造。遂至声乐之泯绝则彼何忍哉。抑何心哉。吾知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1L 页
 其必无是矣。李胡纵横之黍而皆不合。必有所由然也。何其古合而今不合也。愚故曰取黍宜舍僻壤而就中华。退稀贵而进常有。必取其纵些减而横些增者则庶几有得焉耳。何必上党之羊头任城之二米然后为真哉。虽使范公真得周鬯汉龠之秬而以累生分者。终不与千二百之文合矣。范公独未之觉此矣。累黍之法。只是大槩言者也。如淮南之禾蔈,说苑之粟,易纬之马尾,孙子之蚕忽,说文之发。其可一一而准合乎。
其必无是矣。李胡纵横之黍而皆不合。必有所由然也。何其古合而今不合也。愚故曰取黍宜舍僻壤而就中华。退稀贵而进常有。必取其纵些减而横些增者则庶几有得焉耳。何必上党之羊头任城之二米然后为真哉。虽使范公真得周鬯汉龠之秬而以累生分者。终不与千二百之文合矣。范公独未之觉此矣。累黍之法。只是大槩言者也。如淮南之禾蔈,说苑之粟,易纬之马尾,孙子之蚕忽,说文之发。其可一一而准合乎。乐律跋
古今言律者。毕竟不合。则诿之于竹管候气。殊不知候气亦有所不符也。夫律之长短。差以毫分。而试之于气序乖淆之世。如何应之不错乎。隋文帝时尝试之矣。应有早晚。或初八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始应。牛弘却又以气之衰猛为言。猛者臣纵也。衰者君㬥也。帝驳之曰臣纵君㬥。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㬥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盖诸所争。不过秒忽之微。而气候之至。迟速若是不同。其不可以是为断明矣。惜乎。当时万宝常乐谱不传。不得有以考其得失。而其所造水尺律母。黄钟容黍千三百二十。则于千二百之数为近之。然其逆知隋亡。吾未信其必然。使帝亟斥弘等。专仗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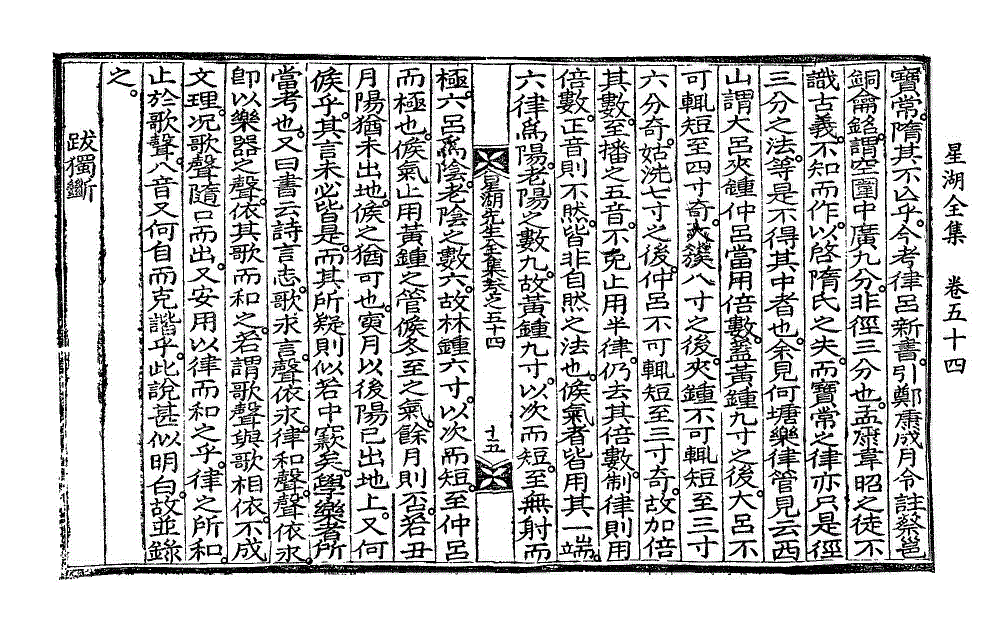 宝常。隋其不亡乎。今考律吕新书。引郑康成月令注蔡邕铜龠铭。谓空围中广九分。非径三分也。孟康韦昭之徒不识古义。不知而作。以启隋氏之失。而宝常之律亦只是径三分之法。等是不得其中者也。余见何塘乐律管见云西山谓大吕夹钟仲吕当用倍数。盖黄钟九寸之后。大吕不可辄短至四寸奇。大簇八寸之后。夹钟不可辄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七寸之后。仲吕不可辄短至三寸奇。故加倍其数。至播之五音。不免止用半律。仍去其倍数。制律则用倍数。正音则不然。皆非自然之法也。候气者皆用其一端。六律为阳。老阳之数九。故黄钟九寸。以次而短。至无射而极。六吕为阴。老阴之数六。故林钟六寸。以次而短。至仲吕而极也。候气止用黄钟之管候冬至之气。馀月则否。若丑月阳犹未出地。候之犹可也。寅月以后阳已出地上。又何候乎。其言未必皆是。而其所疑则似若中窾矣。学乐者所当考也。又曰书云诗言志。歌求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依永。即以乐器之声。依其歌而和之。若谓歌声与歌相依。不成文理。况歌声随口而出。又安用以律而和之乎。律之所和。止于歌声。八音又何自而克谐乎。此说甚似明白。故并录之。
宝常。隋其不亡乎。今考律吕新书。引郑康成月令注蔡邕铜龠铭。谓空围中广九分。非径三分也。孟康韦昭之徒不识古义。不知而作。以启隋氏之失。而宝常之律亦只是径三分之法。等是不得其中者也。余见何塘乐律管见云西山谓大吕夹钟仲吕当用倍数。盖黄钟九寸之后。大吕不可辄短至四寸奇。大簇八寸之后。夹钟不可辄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七寸之后。仲吕不可辄短至三寸奇。故加倍其数。至播之五音。不免止用半律。仍去其倍数。制律则用倍数。正音则不然。皆非自然之法也。候气者皆用其一端。六律为阳。老阳之数九。故黄钟九寸。以次而短。至无射而极。六吕为阴。老阴之数六。故林钟六寸。以次而短。至仲吕而极也。候气止用黄钟之管候冬至之气。馀月则否。若丑月阳犹未出地。候之犹可也。寅月以后阳已出地上。又何候乎。其言未必皆是。而其所疑则似若中窾矣。学乐者所当考也。又曰书云诗言志。歌求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依永。即以乐器之声。依其歌而和之。若谓歌声与歌相依。不成文理。况歌声随口而出。又安用以律而和之乎。律之所和。止于歌声。八音又何自而克谐乎。此说甚似明白。故并录之。跋独断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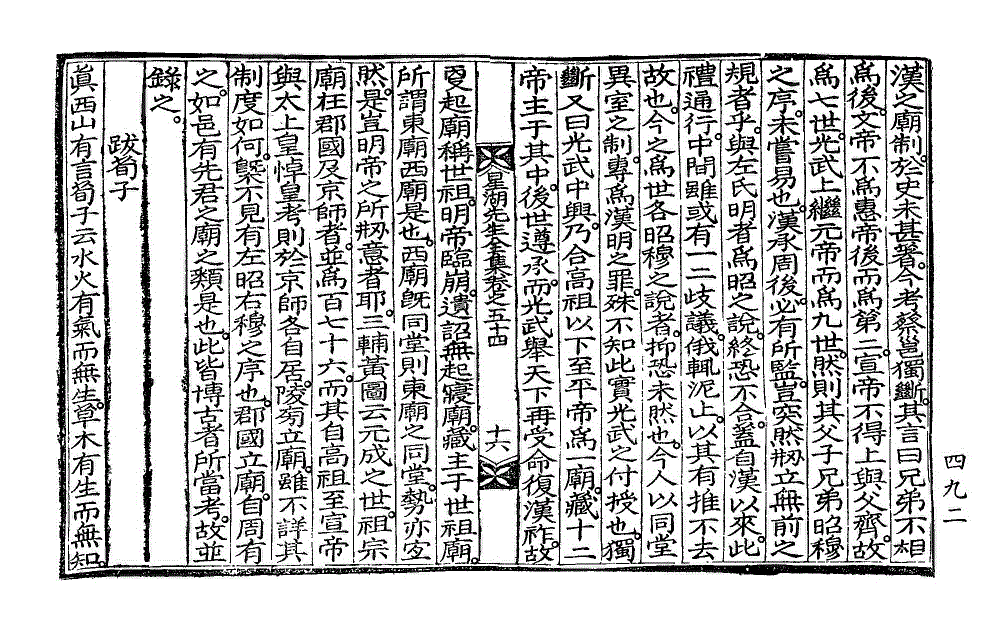 汉之庙制。于史未甚著。今考蔡邕独断。其言曰兄弟不相为后。文帝不为惠帝后而为第二。宣帝不得上与父齐。故为七世。光武上继元帝而为九世。然则其父子兄弟昭穆之序。未尝易也。汉承周后。必有所监。岂突然刱立无前之规者乎。与左氏明者为昭之说。终恐不合。盖自汉以来。此礼通行。中间虽或有一二歧议。俄辄泥止。以其有推不去故也。今之为世各昭穆之说者。抑恐未然也。今人以同堂异室之制。专为汉明之罪。殊不知此实光武之付授也。独断又曰光武中兴。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二帝主于其中。后世遵承。而光武举天下再受命复汉祚。故更起庙称世祖。明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所谓东庙西庙是也。西庙既同堂则东庙之同堂。势亦宜然。是岂明帝之所刱意者耶。三辅黄图云元成之世。祖宗庙在郡国及京师者。并为百七十六。而其自高祖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则于京师各自居。陵旁立庙。虽不详其制度如何。槩不见有左昭右穆之序也。郡国立庙。自周有之。如邑有先君之庙之类是也。此皆博古者所当考。故并录之。
汉之庙制。于史未甚著。今考蔡邕独断。其言曰兄弟不相为后。文帝不为惠帝后而为第二。宣帝不得上与父齐。故为七世。光武上继元帝而为九世。然则其父子兄弟昭穆之序。未尝易也。汉承周后。必有所监。岂突然刱立无前之规者乎。与左氏明者为昭之说。终恐不合。盖自汉以来。此礼通行。中间虽或有一二歧议。俄辄泥止。以其有推不去故也。今之为世各昭穆之说者。抑恐未然也。今人以同堂异室之制。专为汉明之罪。殊不知此实光武之付授也。独断又曰光武中兴。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二帝主于其中。后世遵承。而光武举天下再受命复汉祚。故更起庙称世祖。明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所谓东庙西庙是也。西庙既同堂则东庙之同堂。势亦宜然。是岂明帝之所刱意者耶。三辅黄图云元成之世。祖宗庙在郡国及京师者。并为百七十六。而其自高祖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则于京师各自居。陵旁立庙。虽不详其制度如何。槩不见有左昭右穆之序也。郡国立庙。自周有之。如邑有先君之庙之类是也。此皆博古者所当考。故并录之。跋荀子
真西山有言荀子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3H 页
 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之贵也。此论似矣。盖古今言人物之心者多矣。未有若是之该且明者也。凡言心者知觉之谓也。草木无血气知觉。但有生气则谓之无心可矣。然比类为言则草木亦可谓之心。故语类朱子曰一盆花。得水便敷荣。摧抑便枯悴。谓之无知觉可乎。周茂叔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觉。只是鸟兽底知觉。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觉。不如鸟兽底。然则草木有敷荣枯悴之心而无趋利避害之心矣。鸟兽既有趋利避害之心则虽兼有敷荣枯悴之气。而不复谓之心也。又有所谓好善恶恶之心。此书所谓道心。荀子所谓有义也。心者本只是心脏之知觉。趋利避害好善恶恶。虽有公私之别。其为知觉则同。故均谓之心。而彼生老病痊之类不与焉。由此推之。所谓天地之心者。亦可见天道嘿运而无心者也。虽曰有心。不过与草木之心一般。若曰其喜怒知觉。一如人之应物则岂不亦泥乎哉。夫万物皆天地腹中之有者也。居腹中而能知觉者唯人为然。若曰天地不应无知觉之心。则独人可以当此目。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曰天视听自我民也。论心之说。于斯尽之矣。如荀氏此说。可以表出。不当以性恶礼伪之谬戾而并掩之也。
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之贵也。此论似矣。盖古今言人物之心者多矣。未有若是之该且明者也。凡言心者知觉之谓也。草木无血气知觉。但有生气则谓之无心可矣。然比类为言则草木亦可谓之心。故语类朱子曰一盆花。得水便敷荣。摧抑便枯悴。谓之无知觉可乎。周茂叔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觉。只是鸟兽底知觉。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觉。不如鸟兽底。然则草木有敷荣枯悴之心而无趋利避害之心矣。鸟兽既有趋利避害之心则虽兼有敷荣枯悴之气。而不复谓之心也。又有所谓好善恶恶之心。此书所谓道心。荀子所谓有义也。心者本只是心脏之知觉。趋利避害好善恶恶。虽有公私之别。其为知觉则同。故均谓之心。而彼生老病痊之类不与焉。由此推之。所谓天地之心者。亦可见天道嘿运而无心者也。虽曰有心。不过与草木之心一般。若曰其喜怒知觉。一如人之应物则岂不亦泥乎哉。夫万物皆天地腹中之有者也。居腹中而能知觉者唯人为然。若曰天地不应无知觉之心。则独人可以当此目。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曰天视听自我民也。论心之说。于斯尽之矣。如荀氏此说。可以表出。不当以性恶礼伪之谬戾而并掩之也。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3L 页
 跋启蒙
跋启蒙古书为注家所掩。转益难解者多矣。如胡玉斋启蒙注论算期。以九百四十。分作十九。每分计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丝六忽八秒。十九分内中取七分。总为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忽七丝六秒。如是则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若然月退二十九日则全度之外。馀分之积又一万四十三分一釐五毫七忽四秒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则得十日。馀分又六百四十三分有奇。然则月与日会之间。恰为三十九日有奇。其有此理乎。且其不止于八秒。吾尝试之。历百位而不穷。岂不有违于一章无馀欠之数也。盖月退九百四十者。十二度七分之数也。十二度与十九相乘。纳子七分。为二百三十五。又与四相乘而成者也。然则每度各七十六分。而所谓七分即二十八分。月退二十九日则全度三百四十八。而馀分之积又八百一十二也。如度七十六而一。得十度。馀分五十二也。合成三百五十八度五十二分。置周天之数而相减则馀六度二十四分及四分度之一也。以六度与七十六相乘。纳子二十四则为四百八十。又以四分度之一。与十九相乘合之则为四百九十九。如胡说何异隔靴爬痒。
跋洪范内篇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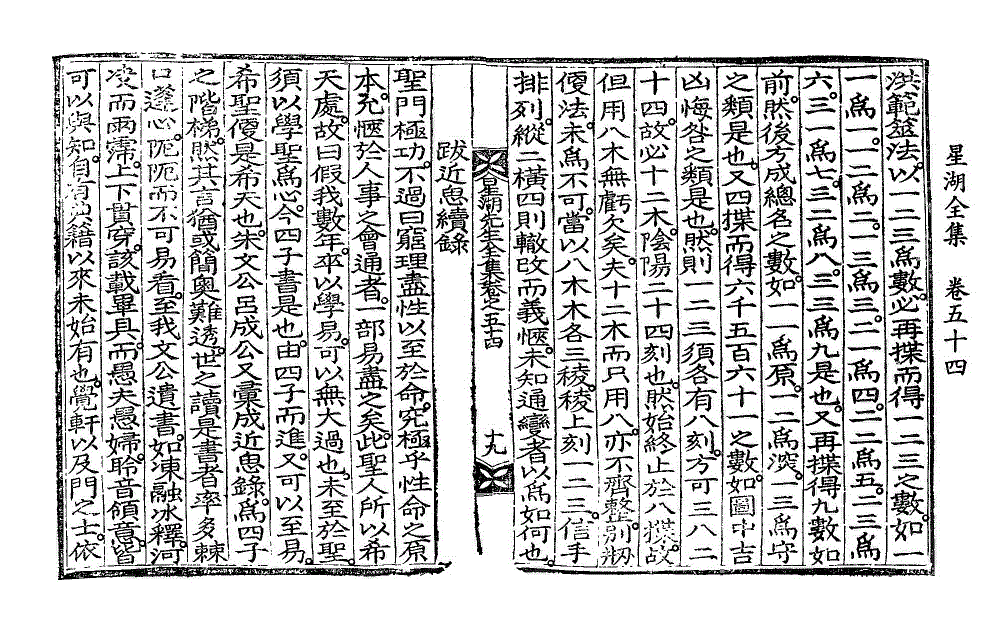 洪范筮法。以一二三为数。必再揲而得一二三之数。如一一为一。一二为二。一三为三。二一为四。二二为五。二三为六。三一为七。三二为八。三三为九是也。又再揲得九数如前。然后方成总名之数。如一一为原。一二为深。一三为守之类是也。又四揲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数。如图中吉凶悔咎之类是也。然则一二三须各有八刻。方可三八二十四。故必十二木。阴阳二十四刻也。然始终止于八揲。故但用八木无亏欠矣。夫十二木而只用八。亦不齐整。别刱便法。未为不可。当以八木木各三棱。棱上刻一二三。信手排列。纵二横四则辙改而义惬。未知通变者以为如何也。
洪范筮法。以一二三为数。必再揲而得一二三之数。如一一为一。一二为二。一三为三。二一为四。二二为五。二三为六。三一为七。三二为八。三三为九是也。又再揲得九数如前。然后方成总名之数。如一一为原。一二为深。一三为守之类是也。又四揲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数。如图中吉凶悔咎之类是也。然则一二三须各有八刻。方可三八二十四。故必十二木。阴阳二十四刻也。然始终止于八揲。故但用八木无亏欠矣。夫十二木而只用八。亦不齐整。别刱便法。未为不可。当以八木木各三棱。棱上刻一二三。信手排列。纵二横四则辙改而义惬。未知通变者以为如何也。跋近思续录
圣门极功。不过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究极乎性命之原本。允惬于人事之会通者。一部易尽之矣。此圣人所以希天处。故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未至于圣。须以学圣为心。今四子书是也。由四子而进。又可以至易。希圣便是希天也。朱文公吕成公又汇成近思录。为四子之阶梯。然其言犹或简奥难透。世之读是书者率多棘口蓬心。阨阨而不可易看。至我文公遗书。如冻融冰释。河决而雨霈。上下贯穿。该载毕具。而愚夫愚妇。聆音领意。皆可以与知。自有典籍以来未始有也。觉轩以及门之士。依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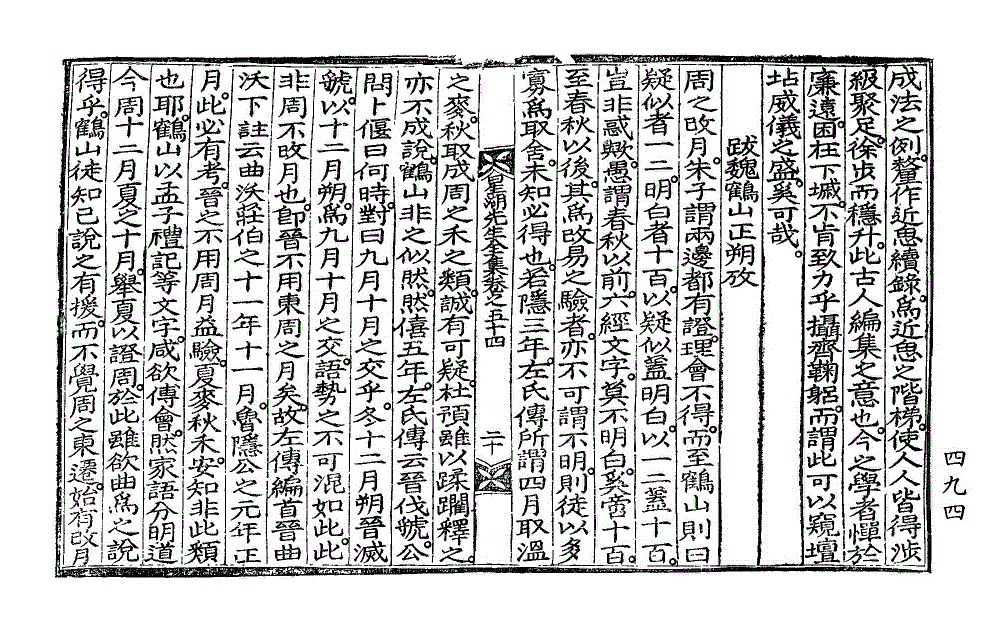 成法之例。釐作近思续录。为近思之阶梯。使人人皆得涉级聚足。徐步而稳升。此古人编集之意也。今之学者惮于廉远。困在下墄。不肯致力乎摄齐鞠躬。而谓此可以窥坛坫威仪之盛。奚可哉。
成法之例。釐作近思续录。为近思之阶梯。使人人皆得涉级聚足。徐步而稳升。此古人编集之意也。今之学者惮于廉远。困在下墄。不肯致力乎摄齐鞠躬。而谓此可以窥坛坫威仪之盛。奚可哉。跋魏鹤山正朔考
周之改月。朱子谓两边都有證。理会不得。而至鹤山则曰疑似者一二。明白者十百。以疑似盖明白。以一二盖十百。岂非惑欤。愚谓春秋以前。六经文字。莫不明白。奚啻十百。至春秋以后。其为改易之验者。亦不可谓不明。则徒以多寡为取舍。未知必得也。若隐三年。左氏传所谓四月取温之麦。秋取成周之禾之类。诚有可疑。杜预虽以蹂躏释之。亦不成说。鹤山非之似然。然僖五年。左氏传云晋伐虢。公问卜偃曰何时。对曰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朔晋灭虢。以十二月朔。为九月十月之交。语势之不可混如此。此非周不改月也。即晋不用东周之月矣。故左传编首晋曲沃下注云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此必有考。晋之不用周月益验。夏麦秋禾。安知非此类也耶。鹤山以孟子礼记等文字。咸欲傅会。然家语分明道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举夏以證周。于此虽欲曲为之说得乎。鹤山徒知己说之有援。而不觉周之东迁。始有改月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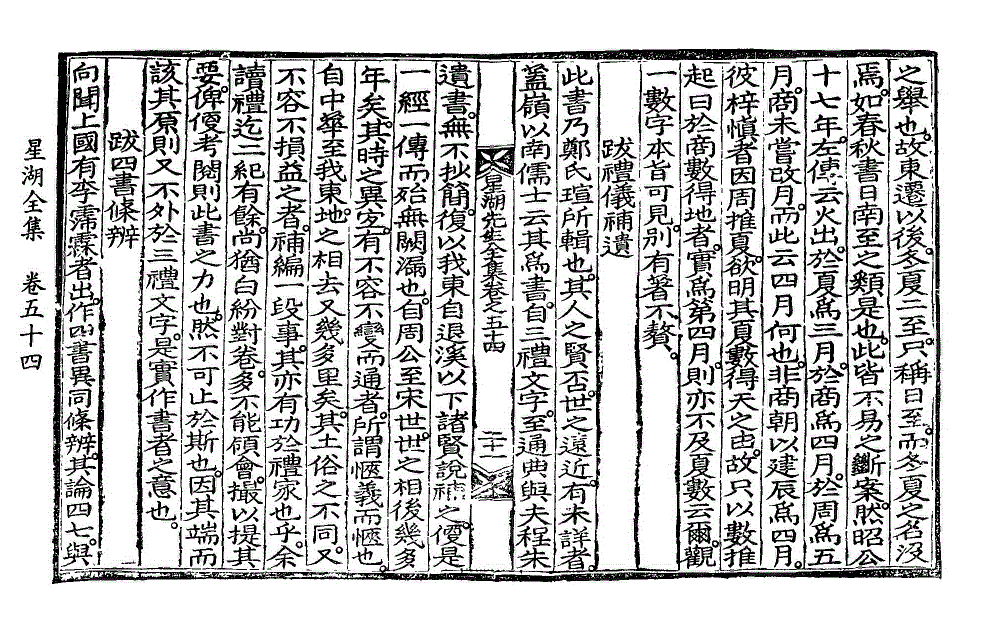 之举也。故东迁以后。冬夏二至。只称日至。而冬夏之名没焉。如春秋书日南至之类是也。此皆不易之断案。然昭公十七年。左传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商未尝改月。而此云四月何也。非商朝以建辰为四月。彼梓慎者因周推夏。欲明其夏数得天之由。故只以数推起曰于商数得地者。实为第四月。则亦不及夏数云尔。观一数字本旨可见。别有著不赘。
之举也。故东迁以后。冬夏二至。只称日至。而冬夏之名没焉。如春秋书日南至之类是也。此皆不易之断案。然昭公十七年。左传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商未尝改月。而此云四月何也。非商朝以建辰为四月。彼梓慎者因周推夏。欲明其夏数得天之由。故只以数推起曰于商数得地者。实为第四月。则亦不及夏数云尔。观一数字本旨可见。别有著不赘。跋礼仪补遗
此书乃郑氏瑄所辑也。其人之贤否。世之远近。有未详者。盖岭以南儒士云其为书。自三礼文字。至通典与夫程朱遗书。无不抄简。复以我东自退溪以下诸贤说补之。便是一经一传而殆无阙漏也。自周公至宋世。世之相后几多年矣。其时之异宜。有不容不变而通者。所谓惬义而惬也。自中华至我东。地之相去又几多里矣。其土俗之不同。又不容不损益之者。补编一段事。其亦有功于礼家也乎。余读礼迄二纪有馀。尚犹白纷对卷。多不能领会。撮以提其要。俾便考阅则此书之力也。然不可止于斯也。因其端而该其原则又不外于三礼文字。是实作书者之意也。
跋四书条辨
向闻上国有李霈霖者出。作四书异同条辨。其论四七。与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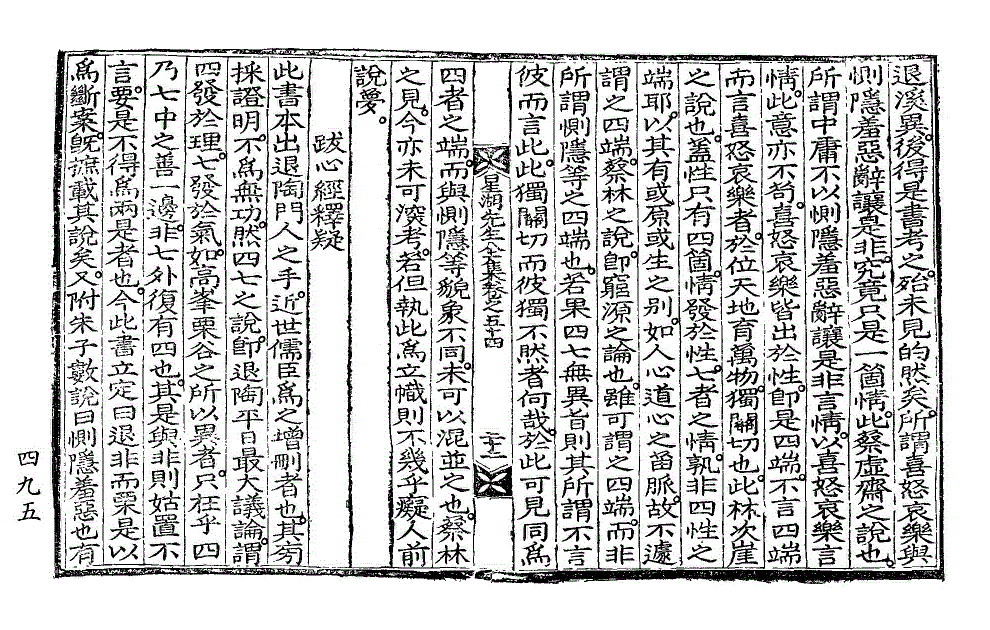 退溪异。后得是书考之。殆未见的然矣。所谓喜怒哀乐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究竟只是一个情。此蔡虚斋之说也。所谓中庸不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言情。以喜怒哀乐言情。此意亦不苟。喜怒哀乐皆出于性。即是四端。不言四端而言喜怒哀乐者。于位天地育万物。独关切也。此林次崖之说也。盖性只有四个。情发于性。七者之情。孰非四性之端耶。以其有或原或生之别。如人心道心之苗脉。故不遽谓之四端。蔡林之说。即穷源之论也。虽可谓之四端。而非所谓恻隐等之四端也。若果四七无异旨则其所谓不言彼而言此。此独关切而彼独不然者何哉。于此可见同为四者之端。而与恻隐等貌象不同。未可以混并之也。蔡林之见。今亦未可深考。若但执此为立帜则不几乎痴人前说梦。
退溪异。后得是书考之。殆未见的然矣。所谓喜怒哀乐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究竟只是一个情。此蔡虚斋之说也。所谓中庸不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言情。以喜怒哀乐言情。此意亦不苟。喜怒哀乐皆出于性。即是四端。不言四端而言喜怒哀乐者。于位天地育万物。独关切也。此林次崖之说也。盖性只有四个。情发于性。七者之情。孰非四性之端耶。以其有或原或生之别。如人心道心之苗脉。故不遽谓之四端。蔡林之说。即穷源之论也。虽可谓之四端。而非所谓恻隐等之四端也。若果四七无异旨则其所谓不言彼而言此。此独关切而彼独不然者何哉。于此可见同为四者之端。而与恻隐等貌象不同。未可以混并之也。蔡林之见。今亦未可深考。若但执此为立帜则不几乎痴人前说梦。跋心经释疑
此书本出退陶门人之手。近世儒臣为之增删者也。其旁采證明。不为无功。然四七之说。即退陶平日最大议论。谓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如高峰栗谷之所以异者。只在乎四乃七中之善一边。非七外复有四也。其是与非则姑置不言。要是不得为两是者也。今此书立定曰退非而栗是以为断案。既摭载其说矣。又附朱子数说曰恻隐羞恶也有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6H 页
 中节不中节。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必须以此足之。然后方为完备。其意欲以栗谷朱子合成完论也。夫四端亦有不善则安在乎七情中善一边者为四端乎。若然七情有善恶。四端亦有善恶。则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信矣。彼所谓四。乃纯善无恶。而七外无四何哉。操戈入室而谓作完备无罅缝可乎。然按退集答李平叔第三书又有可疑。其言曰人心之名。已与道心相对而立。乃属自家体段上私有。落在一边了。不得与道心浑沦为一。至如七情。虽云发于气。然实是公然平立之名。非落在一边底。故乐记中庸好学论中。皆包四端在其中。浑沦而为说也。此说分明与高峰栗谷之意同。然而曰此发于理。彼发于气可乎。其答高峰书气质本然之谕一款。不无后学之疑。今此之论。又是勘合。不知先生所主张果何在耳。又曰子思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若曰人心之未发谓之中则不可。程子谓其中动而七情出。若曰其中动而人心出则不可。愚谓人心者掐著痛爬著痒之类是也。痛痒饥寒之未发。岂非中乎。既有此痛痒饥寒之心则喜怒等之所由生也。痛痒饥寒之中节。即喜怒等之中节。以此为说。恐或无害。且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其中之有动。即触形而发者也。掐痛爬痒亦人心触形而动中者。以此为言。亦
中节不中节。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必须以此足之。然后方为完备。其意欲以栗谷朱子合成完论也。夫四端亦有不善则安在乎七情中善一边者为四端乎。若然七情有善恶。四端亦有善恶。则七情之外复有四端者信矣。彼所谓四。乃纯善无恶。而七外无四何哉。操戈入室而谓作完备无罅缝可乎。然按退集答李平叔第三书又有可疑。其言曰人心之名。已与道心相对而立。乃属自家体段上私有。落在一边了。不得与道心浑沦为一。至如七情。虽云发于气。然实是公然平立之名。非落在一边底。故乐记中庸好学论中。皆包四端在其中。浑沦而为说也。此说分明与高峰栗谷之意同。然而曰此发于理。彼发于气可乎。其答高峰书气质本然之谕一款。不无后学之疑。今此之论。又是勘合。不知先生所主张果何在耳。又曰子思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若曰人心之未发谓之中则不可。程子谓其中动而七情出。若曰其中动而人心出则不可。愚谓人心者掐著痛爬著痒之类是也。痛痒饥寒之未发。岂非中乎。既有此痛痒饥寒之心则喜怒等之所由生也。痛痒饥寒之中节。即喜怒等之中节。以此为说。恐或无害。且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其中之有动。即触形而发者也。掐痛爬痒亦人心触形而动中者。以此为言。亦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6L 页
 恐无害也。向者先生所发明。津津乎四七之分属于道心人心。而至此一书。一皆反之。未知何故也。朱子曰虽言孔子为圣人。须已实见圣处方信。虽退陶之书。既不能言下领意则不可儱侗作已晓说。姑识此以待吾学之进而更考焉。
恐无害也。向者先生所发明。津津乎四七之分属于道心人心。而至此一书。一皆反之。未知何故也。朱子曰虽言孔子为圣人。须已实见圣处方信。虽退陶之书。既不能言下领意则不可儱侗作已晓说。姑识此以待吾学之进而更考焉。退溪礼解跋
世益下。言礼益难。损益不同。土风各异也。礼变则歧。歧则疑。理虽一而节文转繁也。三礼文字。注疏是重。而或不能无失。自家礼之成。群议遂定。然因时制宜。未必皆循周公之旧。至我东退陶子书牍辨答。便是一部家礼。当时典籍不备。欠考者或间之。今人从百代下。勘定百代之因革。非许大力量。固不能也。念昔瀷年少读退陶集。钦悦之馀。觉有前后异说。考不及遍而一时应酬。或妨于垂后。故分门类汇。附以旁證与后来发挥诸说。或添以妄见。其意只要完成一世宪章之渊薮而忘其分。尔来四十有馀年。窃窃焉有望乎并世君子之相与辅成。今禹斯文徵泰费心积劳。亦办一美事。其规模次第。槩与吾书共贯。又往往识其见解。随节中窾。是则瀷之平日跂待而不得者。宁非幸愿。东方有退陶。如周末生圣人。仰如乔泰。信如金石。收拾残简败纸。莫不佩持尊奉。唯恐有异议。然而后生末学。鲁莽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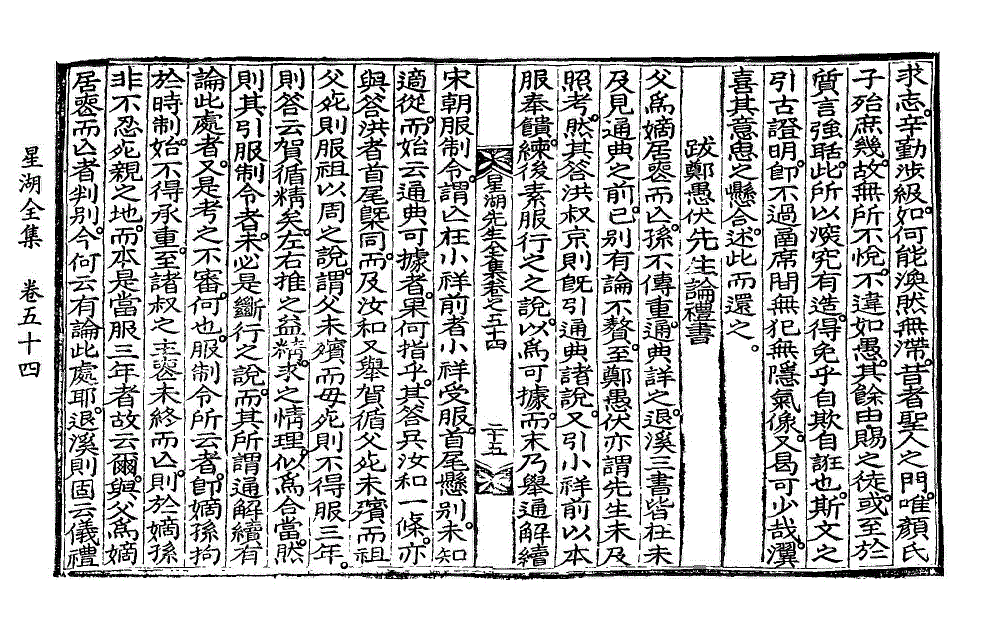 求志。辛勤涉级。如何能涣然无滞。昔者圣人之门。唯颜氏子殆庶几。故无所不悦。不违如愚。其馀由,赐之徒。或至于质言强聒。此所以深究有造。得免乎自欺自诳也。斯文之引古證明。即不过函席间无犯无隐气像。又曷可少哉。瀷喜其意思之悬合。述此而还之。
求志。辛勤涉级。如何能涣然无滞。昔者圣人之门。唯颜氏子殆庶几。故无所不悦。不违如愚。其馀由,赐之徒。或至于质言强聒。此所以深究有造。得免乎自欺自诳也。斯文之引古證明。即不过函席间无犯无隐气像。又曷可少哉。瀷喜其意思之悬合。述此而还之。跋郑愚伏先生论礼书
父为嫡居丧而亡。孙不传重。通典详之。退溪三书皆在未及见通典之前。已别有论不赘。至郑愚伏亦谓先生未及照考。然其答洪叔京则既引通典诸说。又引小祥前以本服奉馈。练后素服行之之说。以为可据。而末乃举通解续宋朝服制令。谓亡在小祥前者小祥受服。首尾悬别。未知适从。而始云通典可据者。果何指乎。其答吴汝和一条。亦与答洪者首尾槩同。而及汝和又举贺循父死未殡而祖父死则服祖以周之说。谓父未殡而母死则不得服三年。则答云贺循精矣。左右推之益精。求之情理。似为合当。然则其引服制令者。未必是断行之说。而其所谓通解续有论此处者。又是考之不审。何也。服制令所云者。即嫡孙拘于时制。始不得承重。至诸叔之主丧未终而亡。则于嫡孙非不忍死亲之地。而本是当服三年者故云尔。与父为嫡居丧而亡者判别。今何云有论此处耶。退溪则固云仪礼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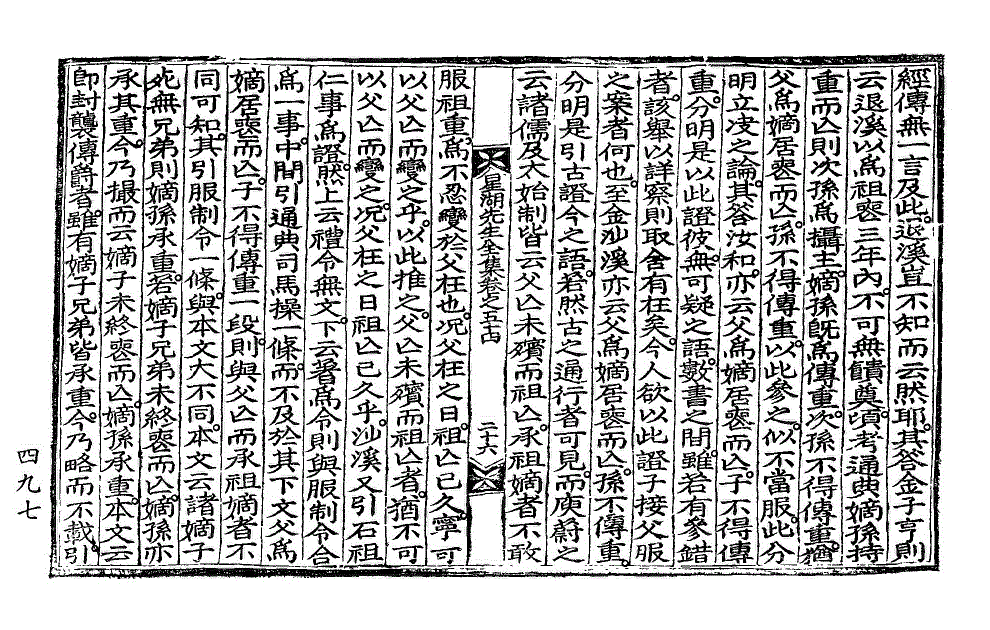 经传无一言及此。退溪岂不知而云然耶。其答金子亨则云退溪以为祖丧三年内。不可无馈奠。顷考通典嫡孙持重而亡则次孙为摄主。嫡孙既为传重。次孙不得传重。犹父为嫡居丧而亡。孙不得传重。以此参之。似不当服。此分明立决之论。其答汝和。亦云父为嫡居丧而亡。子不得传重。分明是以此證彼。无可疑之语。数书之间。虽若有参错者。该举以详察则取舍有在矣。今人欲以此證子接父服之案者何也。至金沙溪亦云父为嫡居丧而亡。孙不传重。分明是引古證今之语。若然古之通行者可见。而庾蔚之云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殡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为不忍变于父在也。况父在之日。祖亡已久。宁可以父亡而变之乎。以此推之。父亡未殡而祖亡者。犹不可以父亡而变之。况父在之日祖亡已久乎。沙溪又引石祖仁事为證。然上云礼令无文。下云著为令则与服制令合为一事。中间引通典司马操一条。而不及于其下文父为嫡居丧而亡。子不得传重一段。则与父亡而承祖嫡者不同可知。其引服制令一条。与本文大不同。本文云诸嫡子死无兄弟则嫡孙承重。若嫡子兄弟未终丧而亡。嫡孙亦承其重。今乃撮而云嫡子未终丧而亡。嫡孙承重。本文云即封袭传爵者。虽有嫡子兄弟皆承重。今乃略而不载。引
经传无一言及此。退溪岂不知而云然耶。其答金子亨则云退溪以为祖丧三年内。不可无馈奠。顷考通典嫡孙持重而亡则次孙为摄主。嫡孙既为传重。次孙不得传重。犹父为嫡居丧而亡。孙不得传重。以此参之。似不当服。此分明立决之论。其答汝和。亦云父为嫡居丧而亡。子不得传重。分明是以此證彼。无可疑之语。数书之间。虽若有参错者。该举以详察则取舍有在矣。今人欲以此證子接父服之案者何也。至金沙溪亦云父为嫡居丧而亡。孙不传重。分明是引古證今之语。若然古之通行者可见。而庾蔚之云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殡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为不忍变于父在也。况父在之日。祖亡已久。宁可以父亡而变之乎。以此推之。父亡未殡而祖亡者。犹不可以父亡而变之。况父在之日祖亡已久乎。沙溪又引石祖仁事为證。然上云礼令无文。下云著为令则与服制令合为一事。中间引通典司马操一条。而不及于其下文父为嫡居丧而亡。子不得传重一段。则与父亡而承祖嫡者不同可知。其引服制令一条。与本文大不同。本文云诸嫡子死无兄弟则嫡孙承重。若嫡子兄弟未终丧而亡。嫡孙亦承其重。今乃撮而云嫡子未终丧而亡。嫡孙承重。本文云即封袭传爵者。虽有嫡子兄弟皆承重。今乃略而不载。引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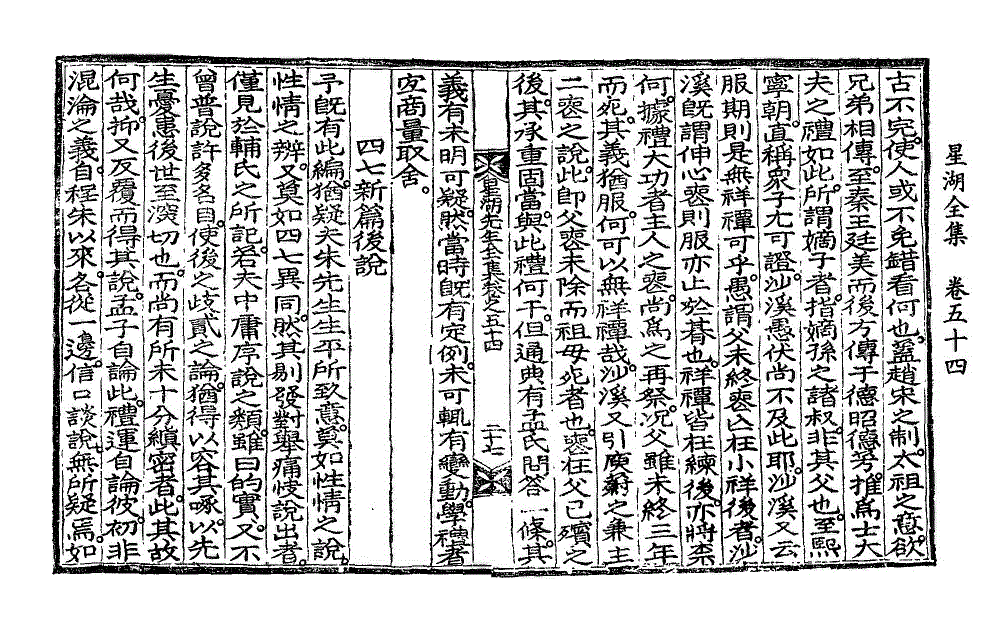 古不完。使人或不免错看何也。盖赵宋之制。太祖之意。欲兄弟相传。至秦王廷美而后方传于德昭德芳。推为士大夫之礼如此。所谓嫡子者。指嫡孙之诸叔。非其父也。至熙宁朝。直称众子尤可證。沙溪愚伏尚不及此耶。沙溪又云服期则是无祥禫可乎。愚谓父未终丧亡在小祥后者。沙溪既谓伸心丧则服亦止于期也。祥禫皆在练后。亦将柰何。据礼大功者主人之丧。尚为之再祭。况父虽未终三年而死。其义犹服。何可以无祥禫哉。沙溪又引庾蔚之兼主二丧之说。此即父丧未除而祖母死者也。丧在父已殡之后。其承重固当。与此礼何干。但通典有孟氏问答一条。其义有未明可疑。然当时既有定例。未可辄有变动。学礼者宜商量取舍。
古不完。使人或不免错看何也。盖赵宋之制。太祖之意。欲兄弟相传。至秦王廷美而后方传于德昭德芳。推为士大夫之礼如此。所谓嫡子者。指嫡孙之诸叔。非其父也。至熙宁朝。直称众子尤可證。沙溪愚伏尚不及此耶。沙溪又云服期则是无祥禫可乎。愚谓父未终丧亡在小祥后者。沙溪既谓伸心丧则服亦止于期也。祥禫皆在练后。亦将柰何。据礼大功者主人之丧。尚为之再祭。况父虽未终三年而死。其义犹服。何可以无祥禫哉。沙溪又引庾蔚之兼主二丧之说。此即父丧未除而祖母死者也。丧在父已殡之后。其承重固当。与此礼何干。但通典有孟氏问答一条。其义有未明可疑。然当时既有定例。未可辄有变动。学礼者宜商量取舍。四七新篇后说
予既有此编。犹疑夫朱先生生平所致意。莫如性情之说。性情之辨。又莫如四七异同。然其剔发对举痛快说出者。仅见于辅氏之所记。若夫中庸序说之类。虽曰的实。又不曾普说许多名目。使后之歧贰之论。犹得以容其喙。以先生忧患后世至深切也。而尚有所未十分缜密者。此其故何哉。抑又反覆而得其说。孟子自论此。礼运自论彼。初非混沦之义。自程朱以来。各从一边。信口谈说。无所疑焉。如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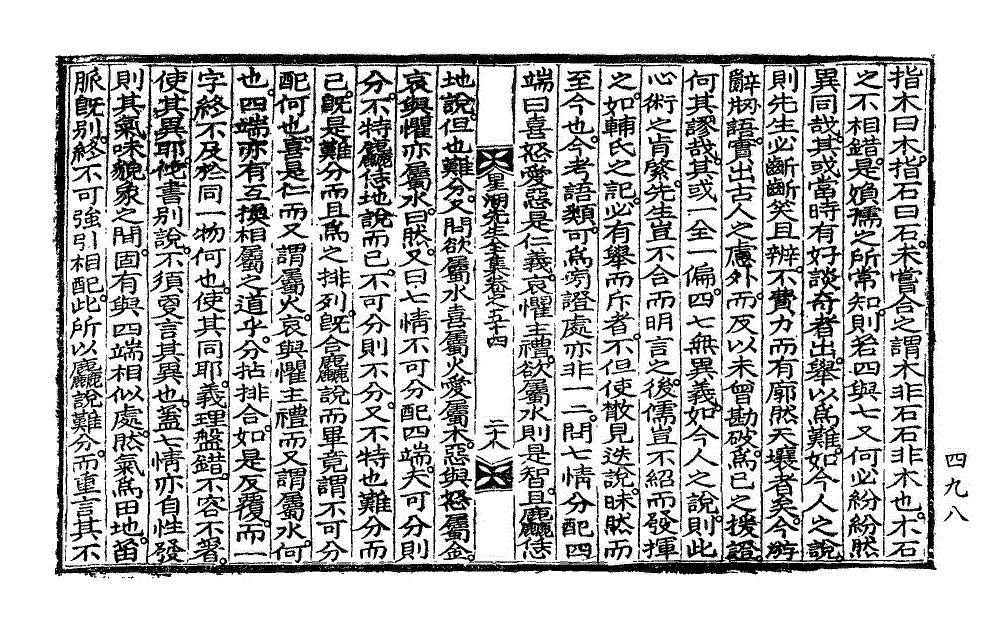 指木曰木。指石曰石。未尝合之谓木非石石非木也。木石之不相错。是妇孺之所常知。则若四与七又何必纷纷然异同哉。其或当时有好谈奇者出。举以为难。如今人之说。则先生必龂龂笑且辨。不费力而有廓然天壤者矣。今游辞刱语。实出古人之虑外。而反以未曾勘破。为己之援證。何其谬哉。其或一全一偏。四七无异义。如今人之说。则此心术之肯綮。先生岂不合而明言之。后儒岂不绍而发挥之。如辅氏之记。必有举而斥者。不但使散见迭说。昧然而至今也。今考语类。可为旁證处亦非一二。问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爱恶是仁义。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粗恁地说。但也难分。又问欲属水喜属火爱属木。恶与怒属金。哀与惧亦属水。曰然。又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夫可分则分。不特粗恁地说而已。不可分则不分。又不特也难分而已。既是难分而且为之排列。既合粗说而毕竟谓不可分配何也。喜是仁而又谓属火。哀与惧主礼而又谓属水。何也。四端亦有互换相属之道乎。分拈排合。如是反覆。而一字终不及于同一物何也。使其同耶。义理盘错。不容不著。使其异耶。佗书别说。不须更言其异也。盖七情亦自性发则其气味貌象之间。固有与四端相似处。然气为田地。苗脉既别。终不可强引相配。此所以粗说难分。而重言其不
指木曰木。指石曰石。未尝合之谓木非石石非木也。木石之不相错。是妇孺之所常知。则若四与七又何必纷纷然异同哉。其或当时有好谈奇者出。举以为难。如今人之说。则先生必龂龂笑且辨。不费力而有廓然天壤者矣。今游辞刱语。实出古人之虑外。而反以未曾勘破。为己之援證。何其谬哉。其或一全一偏。四七无异义。如今人之说。则此心术之肯綮。先生岂不合而明言之。后儒岂不绍而发挥之。如辅氏之记。必有举而斥者。不但使散见迭说。昧然而至今也。今考语类。可为旁證处亦非一二。问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爱恶是仁义。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粗恁地说。但也难分。又问欲属水喜属火爱属木。恶与怒属金。哀与惧亦属水。曰然。又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夫可分则分。不特粗恁地说而已。不可分则不分。又不特也难分而已。既是难分而且为之排列。既合粗说而毕竟谓不可分配何也。喜是仁而又谓属火。哀与惧主礼而又谓属水。何也。四端亦有互换相属之道乎。分拈排合。如是反覆。而一字终不及于同一物何也。使其同耶。义理盘错。不容不著。使其异耶。佗书别说。不须更言其异也。盖七情亦自性发则其气味貌象之间。固有与四端相似处。然气为田地。苗脉既别。终不可强引相配。此所以粗说难分。而重言其不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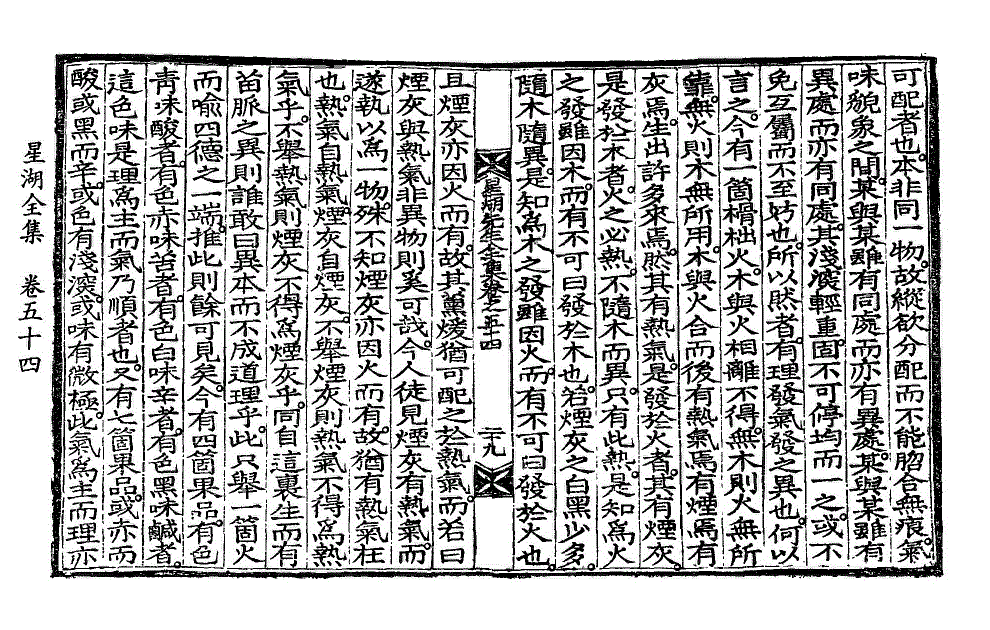 可配者也。本非同一物。故纵欲分配而不能吻合无痕。气味貌象之间。某与某虽有同处而亦有异处。某与某虽有异处而亦有同处。其浅深轻重。固不可停均而一之。或不免互属而不至妨也。所以然者。有理发气发之异也。何以言之。今有一个榾柮火。木与火相离不得。无木则火无所靠。无火则木无所用。木与火合而后有热气焉有烟焉有灰焉。生出许多来焉。然其有热气。是发于火者。其有烟灰。是发于木者。火之必热。不随木而异。只有此热。是知为火之发虽因木。而有不可曰发于木也。若烟灰之白黑少多。随木随异。是知为木之发虽因火。而有不可曰发于火也。且烟灰亦因火而有。故其薰煖犹可配之于热气。而若曰烟灰与热气非异物则奚可哉。今人徒见烟灰有热气。而遂执以为一物。殊不知烟灰亦因火而有。故犹有热气在也。热气自热气。烟灰自烟灰。不举烟灰则热气不得为热气乎。不举热气则烟灰不得为烟灰乎。同自这里生而有苗脉之异则谁敢曰异本而不成道理乎。此只举一个火而喻四德之一端。推此则馀可见矣。今有四个果品。有色青味酸者。有色赤味苦者。有色白味辛者。有色黑味咸者。这色味是理为主而气乃顺者也。又有七个果品。或赤而酸或黑而辛。或色有浅深。或味有微极。此气为主而理亦
可配者也。本非同一物。故纵欲分配而不能吻合无痕。气味貌象之间。某与某虽有同处而亦有异处。某与某虽有异处而亦有同处。其浅深轻重。固不可停均而一之。或不免互属而不至妨也。所以然者。有理发气发之异也。何以言之。今有一个榾柮火。木与火相离不得。无木则火无所靠。无火则木无所用。木与火合而后有热气焉有烟焉有灰焉。生出许多来焉。然其有热气。是发于火者。其有烟灰。是发于木者。火之必热。不随木而异。只有此热。是知为火之发虽因木。而有不可曰发于木也。若烟灰之白黑少多。随木随异。是知为木之发虽因火。而有不可曰发于火也。且烟灰亦因火而有。故其薰煖犹可配之于热气。而若曰烟灰与热气非异物则奚可哉。今人徒见烟灰有热气。而遂执以为一物。殊不知烟灰亦因火而有。故犹有热气在也。热气自热气。烟灰自烟灰。不举烟灰则热气不得为热气乎。不举热气则烟灰不得为烟灰乎。同自这里生而有苗脉之异则谁敢曰异本而不成道理乎。此只举一个火而喻四德之一端。推此则馀可见矣。今有四个果品。有色青味酸者。有色赤味苦者。有色白味辛者。有色黑味咸者。这色味是理为主而气乃顺者也。又有七个果品。或赤而酸或黑而辛。或色有浅深。或味有微极。此气为主而理亦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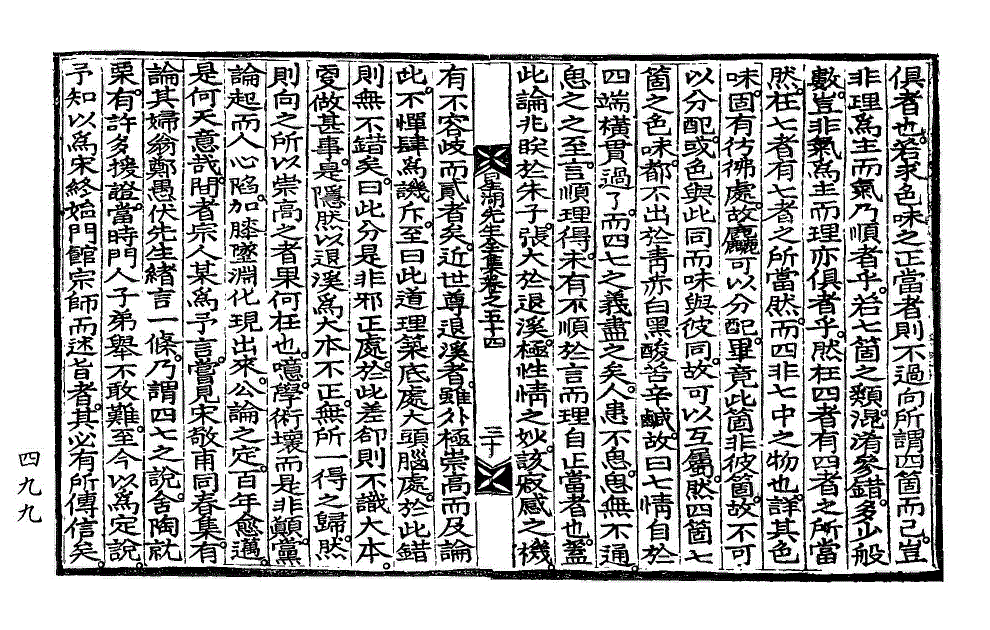 俱者也。若求色味之正当者则不过向所谓四个而已。岂非理为主而气乃顺者乎。若七个之类。混淆参错。多少般数。岂非气为主而理亦俱者乎。然在四者有四者之所当然。在七者有七者之所当然。而四非七中之物也。详其色味。固有彷佛处。故粗可以分配。毕竟此个非彼个。故不可以分配。或色与此同而味与彼同。故可以互属。然四个七个之色味。都不出于青赤白黑酸苦辛咸。故曰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而四七之义尽之矣。人患不思。思无不通。思之之至。言顺理得。未有不顺于言而理自正当者也。盖此论兆眹于朱子。张大于退溪。极性情之妙。该寂感之机。有不容歧而贰者矣。近世尊退溪者。虽外极崇高而及论此。不惮肆为讥斥。至曰此道理筑底处大头脑处。于此错则无不错矣。曰此分是非邪正处。于此差却则不识大本。更做甚事。是隐然以退溪为大本不正。无所一得之归。然则向之所以崇高之者果何在也。噫。学术坏而是非颠。党论起而人心陷。加膝坠渊化现出来。公论之定。百年愈迈。是何天意哉。间者宗人某为予言。尝见宋敬甫同春集。有论其妇翁郑愚伏先生绪言一条。乃谓四七之说。舍陶就栗。有许多援證。当时门人子弟举不敢难。至今以为定说。予知以为宋终始门馆宗师而述旨者。其必有所传信矣。
俱者也。若求色味之正当者则不过向所谓四个而已。岂非理为主而气乃顺者乎。若七个之类。混淆参错。多少般数。岂非气为主而理亦俱者乎。然在四者有四者之所当然。在七者有七者之所当然。而四非七中之物也。详其色味。固有彷佛处。故粗可以分配。毕竟此个非彼个。故不可以分配。或色与此同而味与彼同。故可以互属。然四个七个之色味。都不出于青赤白黑酸苦辛咸。故曰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而四七之义尽之矣。人患不思。思无不通。思之之至。言顺理得。未有不顺于言而理自正当者也。盖此论兆眹于朱子。张大于退溪。极性情之妙。该寂感之机。有不容歧而贰者矣。近世尊退溪者。虽外极崇高而及论此。不惮肆为讥斥。至曰此道理筑底处大头脑处。于此错则无不错矣。曰此分是非邪正处。于此差却则不识大本。更做甚事。是隐然以退溪为大本不正。无所一得之归。然则向之所以崇高之者果何在也。噫。学术坏而是非颠。党论起而人心陷。加膝坠渊化现出来。公论之定。百年愈迈。是何天意哉。间者宗人某为予言。尝见宋敬甫同春集。有论其妇翁郑愚伏先生绪言一条。乃谓四七之说。舍陶就栗。有许多援證。当时门人子弟举不敢难。至今以为定说。予知以为宋终始门馆宗师而述旨者。其必有所传信矣。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500H 页
 一日偶阅愚伏集。其答曹汝益书曰理之发气之发云者。特各以其主张者言之耳。非谓四端无气而七情无理也。今人欲以喜怒哀乐分配于仁义礼智者。尤觉牵强。七情自七情。四端自四端。恐不可相合也。确乎言哉。如此其不可易也。及其殁。不再传而异说起。至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习闻其说者。或笔之于书曰吾师亦尝云尔。呜呼。不察而已矣。夫四七之为世大议论者久矣。设使先生旋言旋改。果有取栗之举。诸门人子弟皆不得与闻。而独密付单传。未尝一字见于频繁往复之间。待易箦然后始乃腾诸口耳。把作把柄者何哉。向者以退溪之望。尚不能解一时之惑。今愚伏要亦非圣人地位。未必据以为定论。然揍无作有。簧鼓众舌。举一世迷其是非之真。则不无操其机者存焉。是甚可叹。予又见赵圣期拙脩集。槩立脚于退门。然有曰唯退溪之内出外感等语则自不是。其佗立言。此皮而彼骨。依然是栗谷馀波矣。盖内出外感四字。本非退门成说。乃栗谷妆定硬说云退翁之见。有内出外感之差也。勒成公案。垂诸后生。后之宗此论者。不能深考。意若真有是说者然。蔽陷既久。不复可得以谕解矣。然当时言语文字。班班不爽。唯一种有真眼者可以覈之得其实矣。彼拙脩公尊尚之笃。犹不免如此骨突。况世之靡靡乎入
一日偶阅愚伏集。其答曹汝益书曰理之发气之发云者。特各以其主张者言之耳。非谓四端无气而七情无理也。今人欲以喜怒哀乐分配于仁义礼智者。尤觉牵强。七情自七情。四端自四端。恐不可相合也。确乎言哉。如此其不可易也。及其殁。不再传而异说起。至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习闻其说者。或笔之于书曰吾师亦尝云尔。呜呼。不察而已矣。夫四七之为世大议论者久矣。设使先生旋言旋改。果有取栗之举。诸门人子弟皆不得与闻。而独密付单传。未尝一字见于频繁往复之间。待易箦然后始乃腾诸口耳。把作把柄者何哉。向者以退溪之望。尚不能解一时之惑。今愚伏要亦非圣人地位。未必据以为定论。然揍无作有。簧鼓众舌。举一世迷其是非之真。则不无操其机者存焉。是甚可叹。予又见赵圣期拙脩集。槩立脚于退门。然有曰唯退溪之内出外感等语则自不是。其佗立言。此皮而彼骨。依然是栗谷馀波矣。盖内出外感四字。本非退门成说。乃栗谷妆定硬说云退翁之见。有内出外感之差也。勒成公案。垂诸后生。后之宗此论者。不能深考。意若真有是说者然。蔽陷既久。不复可得以谕解矣。然当时言语文字。班班不爽。唯一种有真眼者可以覈之得其实矣。彼拙脩公尊尚之笃。犹不免如此骨突。况世之靡靡乎入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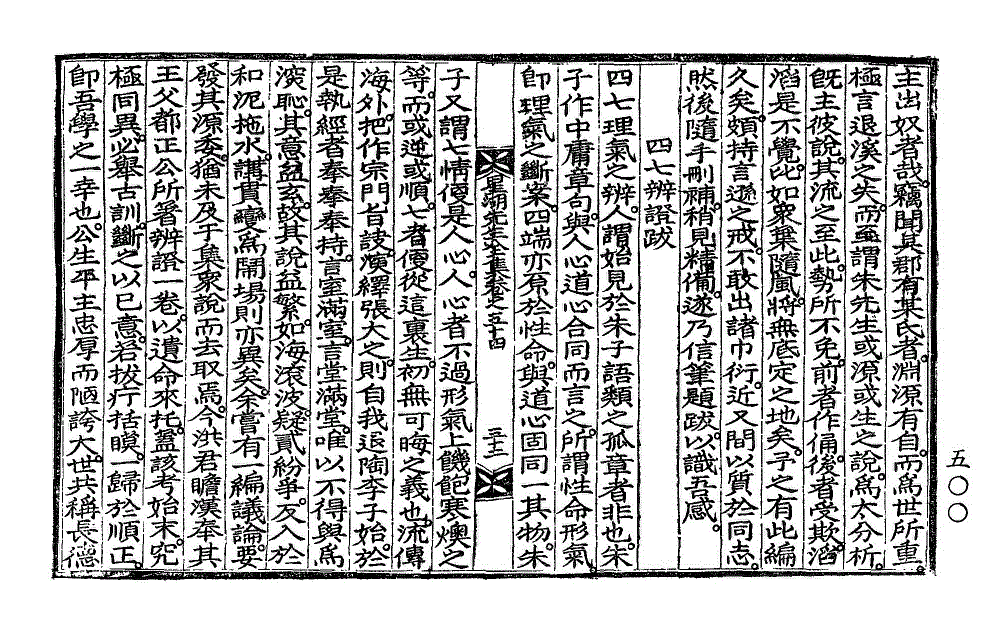 主出奴者哉。窃闻某郡有某氏者。渊源有自。而为世所重。极言退溪之失。而至谓朱先生或源或生之说。为太分析。既主彼说。其流之至此。势所不免。前者作俑。后者受欺。滔滔是不觉。比如众叶随风。将无底定之地矣。予之有此编久矣。颇持言逊之戒。不敢出诸巾衍。近又间以质于同志。然后随手删补。稍见精备。遂乃信笔题跋。以识吾感。
主出奴者哉。窃闻某郡有某氏者。渊源有自。而为世所重。极言退溪之失。而至谓朱先生或源或生之说。为太分析。既主彼说。其流之至此。势所不免。前者作俑。后者受欺。滔滔是不觉。比如众叶随风。将无底定之地矣。予之有此编久矣。颇持言逊之戒。不敢出诸巾衍。近又间以质于同志。然后随手删补。稍见精备。遂乃信笔题跋。以识吾感。四七辨證跋
四七理气之辨。人谓始见于朱子语类之孤章者非也。朱子作中庸章句。与人心道心合同而言之。所谓性命形气。即理气之断案。四端亦原于性命。与道心固同一其物。朱子又谓七情便是人心。人心者不过形气上饥饱寒燠之等。而或逆或顺。七者便从这里生。初无可晦之义也。流传海外。把作宗门旨诀。演绎张大之。则自我退陶李子始。于是执经者拳拳奉持。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唯以不得与为深耻。其意益玄。故其说益繁。如海滚波。疑贰纷争。反入于和泥拖水。讲贯变为闹场则亦异矣。余尝有一编议论。要发其源委。犹未及于集众说而去取焉。今洪君瞻汉奉其王父都正公所著辨證一卷。以遗命来托。盖该考始末。究极同异。必举古训。断之以己意。若拔疔括瞙。一归于顺正。即吾学之一幸也。公生平主忠厚而陋誇大。世共称长德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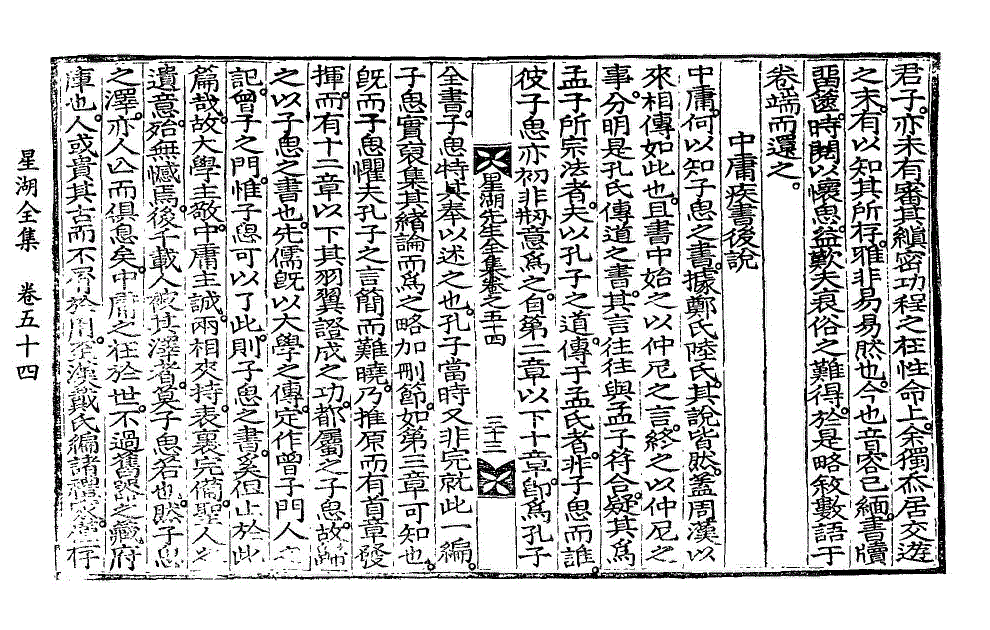 君子。亦未有审其缜密功程之在性命上。余独忝居交游之末。有以知其所存。雅非易易然也。今也音容已缅。书牍留箧。时阅以怀思。益叹夫衰俗之难得。于是略叙数语于卷端而还之。
君子。亦未有审其缜密功程之在性命上。余独忝居交游之末。有以知其所存。雅非易易然也。今也音容已缅。书牍留箧。时阅以怀思。益叹夫衰俗之难得。于是略叙数语于卷端而还之。中庸疾书后说
中庸。何以知子思之书。据郑氏陆氏。其说皆然。盖周汉以来相传如此也。且书中始之以仲尼之言。终之以仲尼之事。分明是孔氏传道之书。其言往往与孟子符合。疑其为孟子所宗法者。夫以孔子之道。传于孟氏者。非子思而谁。彼子思亦初非刱意为之。自第二章以下十章。即为孔子全书。子思特其奉以述之也。孔子当时又非完就此一编。子思实裒集其绪论而为之略加删节。如第三章可知也。既而子思惧夫孔子之言简而难晓。乃推原而有首章发挥。而有十二章以下其羽翼證成之功。都属之子思。故归之以子思之书也。先儒既以大学之传。定作曾子门人之记。曾子之门。惟子思可以了此。则子思之书。奚但止于此篇哉。故大学主敬。中庸主诚。两相夹持。表里完备。圣人之遗意。殆无憾焉。后千载人被其泽者。莫子思若也。然子思之泽。亦人亡而俱息矣。中庸之在于世。不过旧器之藏府库也。人或贵其古而不屑于用。至汉戴氏编诸礼家。仅存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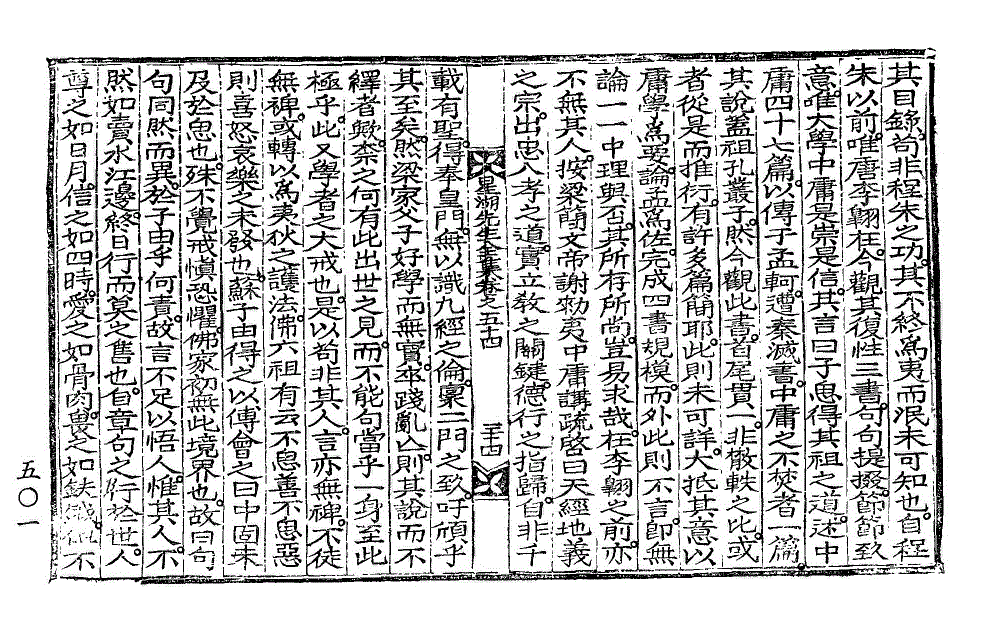 其目录。苟非程朱之功。其不终为夷而泯未可知也。自程朱以前。唯唐李翱在。今观其复性三书。句句提掇。节节致意。唯大学中庸是崇是信。其言曰子思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其说盖祖孔丛子。然今观此书。首尾贯一。非散轶之比。或者从是而推衍。有许多篇简耶。此则未可详。大抵其意以庸学为要。论孟为佐。完成四书规模。而外此则不言。即无论一一中理与否。其所存所尚。岂易求哉。在李翱之前。亦不无其人。按梁简文帝谢敕夷中庸讲疏启曰天经地义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实立教之关键。德行之指归。自非千载有圣。得奉皇门。无以识九经之伦。禀二门之致。吁颀乎其至矣。然梁家父子好学而无实。卒践乱亡。则其说而不绎者欤。柰之何有此出世之见。而不能句当乎一身至此极乎。此又学者之大戒也。是以苟非其人。言亦无裨。不徒无裨。或转以为夷狄之护法。佛六祖有云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苏子由得之以傅会之曰中固未及于思也。殊不觉戒慎恐惧。佛家初无此境界也。故曰句句同然而异。于子由乎何责。故言不足以悟人。惟其人。不然如卖水江边。终日行而莫之售也。自章句之行于世。人尊之如日月。信之如四时。爱之如骨肉。畏之如鈇钺。但不
其目录。苟非程朱之功。其不终为夷而泯未可知也。自程朱以前。唯唐李翱在。今观其复性三书。句句提掇。节节致意。唯大学中庸是崇是信。其言曰子思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其说盖祖孔丛子。然今观此书。首尾贯一。非散轶之比。或者从是而推衍。有许多篇简耶。此则未可详。大抵其意以庸学为要。论孟为佐。完成四书规模。而外此则不言。即无论一一中理与否。其所存所尚。岂易求哉。在李翱之前。亦不无其人。按梁简文帝谢敕夷中庸讲疏启曰天经地义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实立教之关键。德行之指归。自非千载有圣。得奉皇门。无以识九经之伦。禀二门之致。吁颀乎其至矣。然梁家父子好学而无实。卒践乱亡。则其说而不绎者欤。柰之何有此出世之见。而不能句当乎一身至此极乎。此又学者之大戒也。是以苟非其人。言亦无裨。不徒无裨。或转以为夷狄之护法。佛六祖有云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苏子由得之以傅会之曰中固未及于思也。殊不觉戒慎恐惧。佛家初无此境界也。故曰句句同然而异。于子由乎何责。故言不足以悟人。惟其人。不然如卖水江边。终日行而莫之售也。自章句之行于世。人尊之如日月。信之如四时。爱之如骨肉。畏之如鈇钺。但不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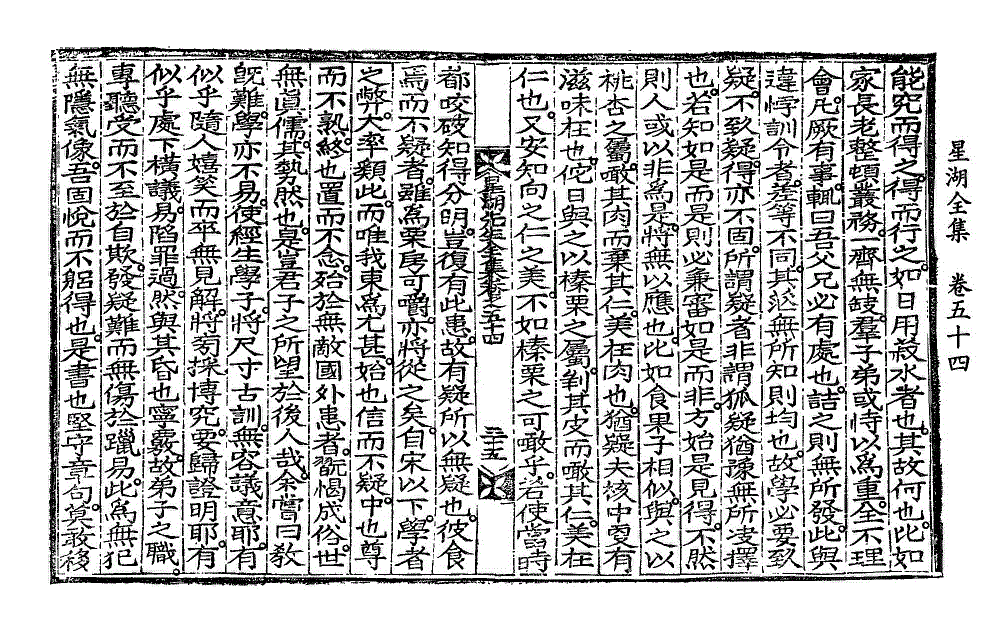 能究而得之。得而行之。如日用菽水者也。其故何也。比如家长老整顿丛务。一齐无缺。群子弟或恃以为重。全不理会。凡厥有事。辄曰吾父兄必有处也。诘之则无所发。此与违悖训令者。差等不同。其茫无所知则均也。故学必要致疑。不致疑。得亦不固。所谓疑者非谓狐疑犹豫无所决择也。若知如是而是则必兼审如是而非。方始是见得。不然则人或以非为是。将无以应也。比如食果子相似。与之以桃杏之属。啖其肉而弃其仁。美在肉也。犹疑夫核中更有滋味在也。佗日与之以榛栗之属。剥其皮而啖其仁。美在仁也。又安知向之仁之美。不如榛栗之可啖乎。若使当时都咬破知得分明。岂复有此患。故有疑所以无疑也。彼食焉而不疑者。虽为栗房可嚼。亦将从之矣。自宋以下。学者之弊。大率类此。而唯我东为尤甚。始也信而不疑。中也尊而不熟。终也置而不念。殆于无敌国外患者。玩愒成俗。世无真儒。其势然也。是岂君子之所望于后人哉。余尝曰教既难。学亦不易。使经生学子。将尺寸古训。无容议意耶。有似乎随人嬉笑而卒无见解。将旁采博究。要归證明耶。有似乎处下横议。易陷罪过。然与其昏也宁覈。故弟子之职。专听受而不至于自欺。发疑难而无伤于躐易。此为无犯无隐气像。吾固悦而不躬得也。是书也坚守章句。莫敢移
能究而得之。得而行之。如日用菽水者也。其故何也。比如家长老整顿丛务。一齐无缺。群子弟或恃以为重。全不理会。凡厥有事。辄曰吾父兄必有处也。诘之则无所发。此与违悖训令者。差等不同。其茫无所知则均也。故学必要致疑。不致疑。得亦不固。所谓疑者非谓狐疑犹豫无所决择也。若知如是而是则必兼审如是而非。方始是见得。不然则人或以非为是。将无以应也。比如食果子相似。与之以桃杏之属。啖其肉而弃其仁。美在肉也。犹疑夫核中更有滋味在也。佗日与之以榛栗之属。剥其皮而啖其仁。美在仁也。又安知向之仁之美。不如榛栗之可啖乎。若使当时都咬破知得分明。岂复有此患。故有疑所以无疑也。彼食焉而不疑者。虽为栗房可嚼。亦将从之矣。自宋以下。学者之弊。大率类此。而唯我东为尤甚。始也信而不疑。中也尊而不熟。终也置而不念。殆于无敌国外患者。玩愒成俗。世无真儒。其势然也。是岂君子之所望于后人哉。余尝曰教既难。学亦不易。使经生学子。将尺寸古训。无容议意耶。有似乎随人嬉笑而卒无见解。将旁采博究。要归證明耶。有似乎处下横议。易陷罪过。然与其昏也宁覈。故弟子之职。专听受而不至于自欺。发疑难而无伤于躐易。此为无犯无隐气像。吾固悦而不躬得也。是书也坚守章句。莫敢移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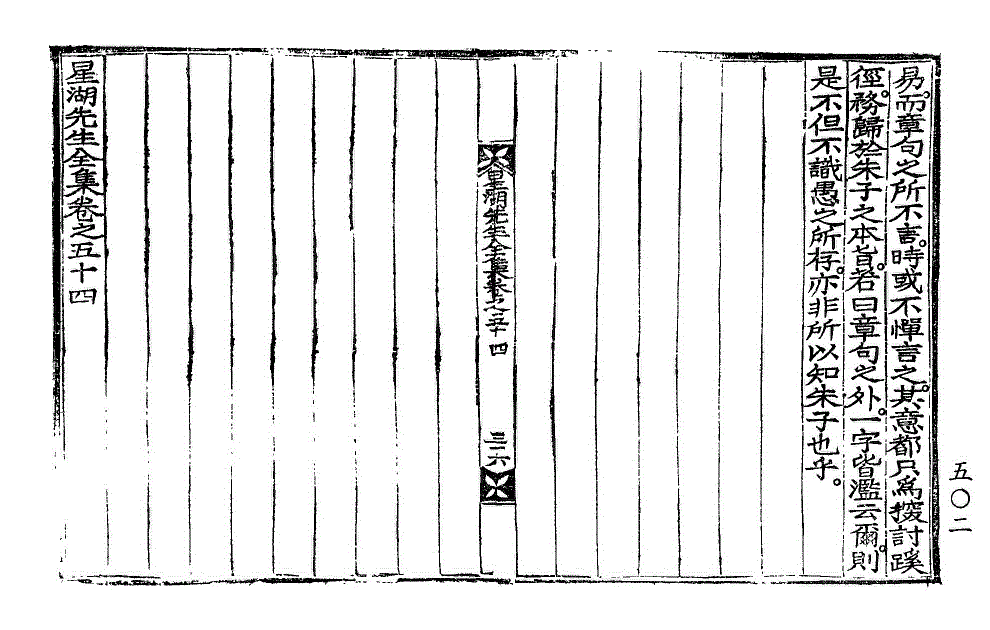 易。而章句之所不言。时或不惮言之。其意都只为探讨蹊径。务归于朱子之本旨。若曰章句之外。一字皆滥云尔。则是不但不识愚之所存。亦非所以知朱子也乎。
易。而章句之所不言。时或不惮言之。其意都只为探讨蹊径。务归于朱子之本旨。若曰章句之外。一字皆滥云尔。则是不但不识愚之所存。亦非所以知朱子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