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恕庵集卷之十一(平山申靖夏正甫 著)
记
记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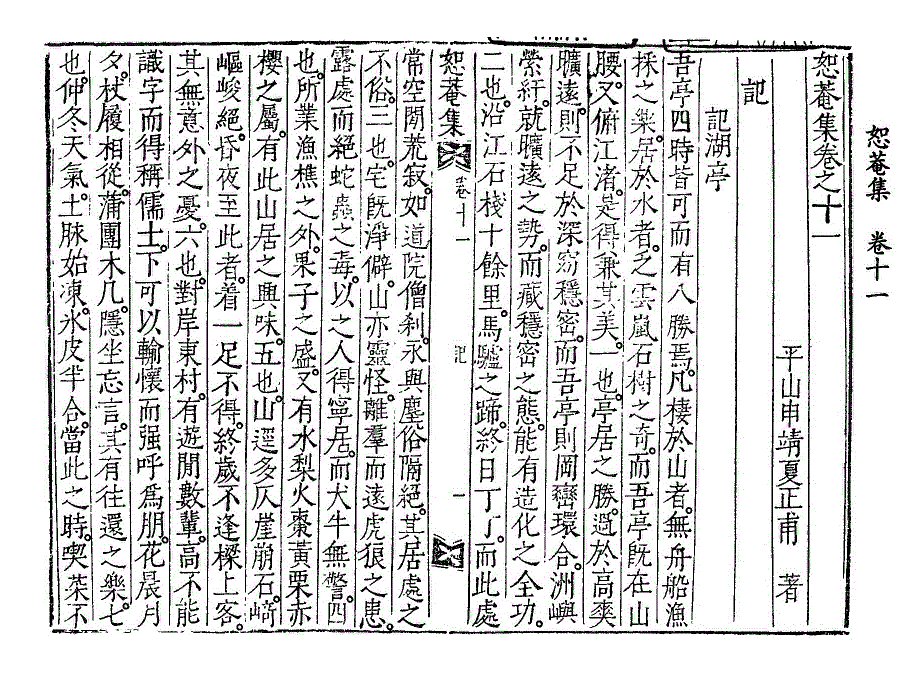 记湖亭
记湖亭吾亭四时皆可而有八胜焉。凡栖于山者。无舟船渔采之乐。居于水者。乏云岚石树之奇。而吾亭既在山腰。又俯江渚。是得兼其美。一也。亭居之胜。过于高爽旷远。则不足于深窈稳密。而吾亭则冈峦环合。洲屿萦纡。就旷远之势。而藏稳密之态。能有造化之全功。二也。沿江石栈十馀里。马驴之蹄。终日丁丁。而此处常空閒荒寂。如道院僧刹。永与尘俗隔绝。其居处之不俗。三也。宅既净僻。山亦灵怪。离群而远虎狼之患。露处而绝蛇虫之毒。以之人得宁居。而犬牛无警。四也。所业渔樵之外。果子之盛。又有水梨火枣黄栗赤樱之属。有此山居之兴味。五也。山径多仄崖崩石。崎岖峻绝。昏夜至此者。着一足不得。终岁不逢梁上客。其无意外之忧。六也。对岸东村。有游閒数辈。高不能识字而得称儒士。下可以输怀而强呼为朋。花晨月夕。杖履相从。蒲团木几。隐坐忘言。其有往还之乐。七也。仲冬天气。土脉始冻。冰皮半合。当此之时。吃菜不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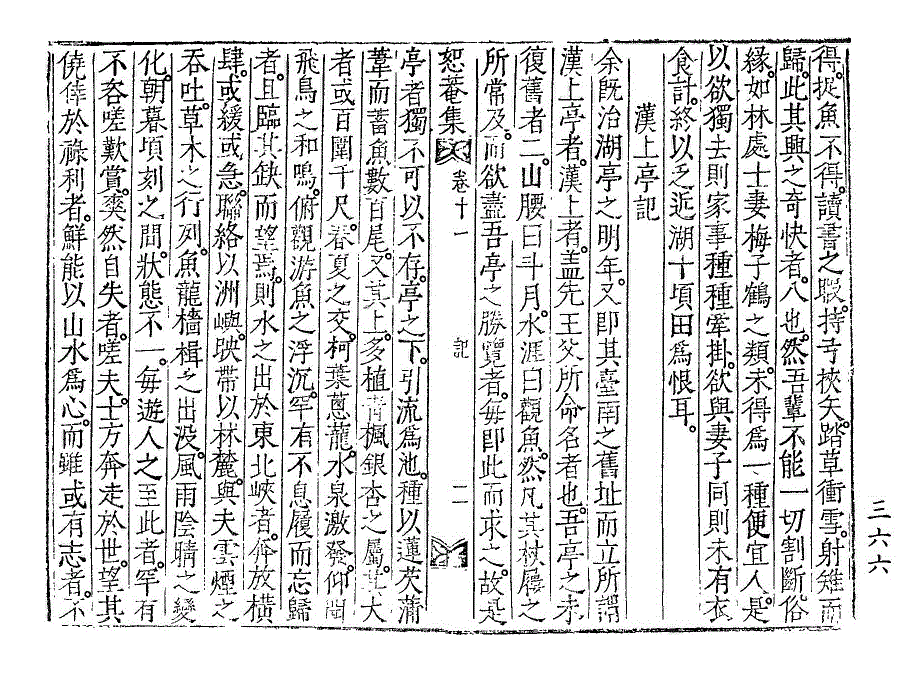 得。捉鱼不得。读书之暇。持弓挟矢。踏草冲雪。射雉而归。此其兴之奇快者。八也。然吾辈不能一切割断俗缘。如林处士妻梅子鹤之类。未得为一种便宜人。是以欲独去则家事种种牵挂。欲与妻子同则未有衣食计。终以乏近湖十顷田为恨耳。
得。捉鱼不得。读书之暇。持弓挟矢。踏草冲雪。射雉而归。此其兴之奇快者。八也。然吾辈不能一切割断俗缘。如林处士妻梅子鹤之类。未得为一种便宜人。是以欲独去则家事种种牵挂。欲与妻子同则未有衣食计。终以乏近湖十顷田为恨耳。汉上亭记
余既治湖亭之明年。又即其台南之旧址而立所谓汉上亭者。汉上者。盖先王父所命名者也。吾亭之未复旧者二。山腰曰斗月。水涯曰观鱼。然凡其杖屦之所常及。而欲尽吾亭之胜览者。每即此而求之。故是亭者独不可以不存。亭之下。引流为池。种以莲芡蒲苇而蓄鱼数百尾。又其上。多植青枫银杏之属。其大者或百围千尺。春夏之交。柯叶葱茏。水泉激发。仰闻飞鸟之和鸣。俯观游鱼之浮沉。罕有不息履而忘归者。且临其缺而望焉。则水之出于东北峡者。奔放横肆。或缓或急。联络以洲屿。映带以林麓。与夫云烟之吞吐。草木之行列。鱼龙樯楫之出没。风雨阴晴之变化。朝暮顷刻之间。状态不一。每游人之至此者。罕有不咨嗟叹赏。爽然自失者。嗟夫。士方奔走于世。望其侥倖于禄利者。鲜能以山水为心。而虽或有志者。不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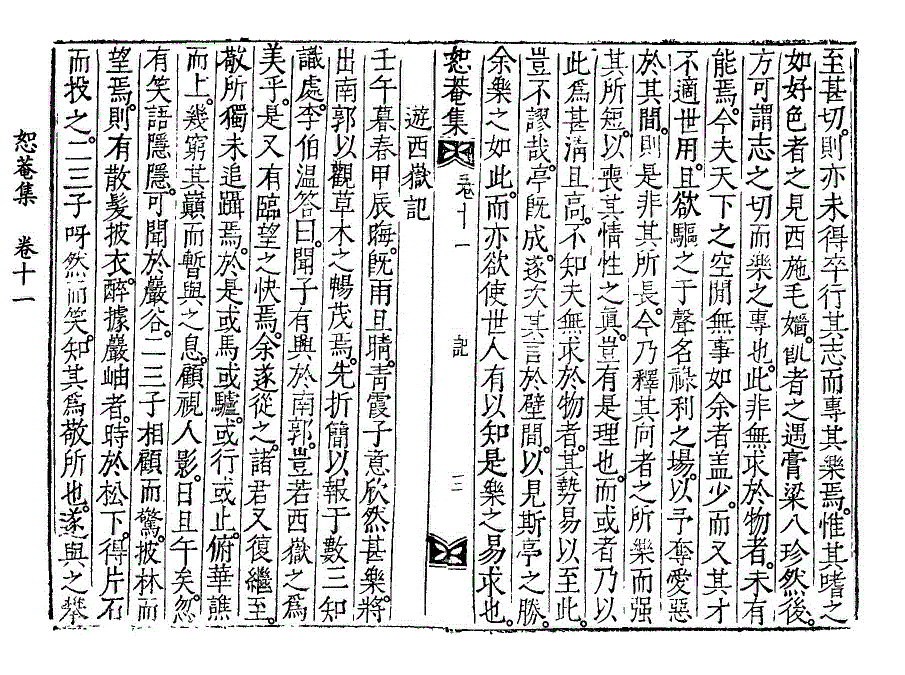 至甚切。则亦未得卒行其志而专其乐焉。惟其嗜之如好色者之见西施毛嫱。饥者之遇膏粱八珍然后。方可谓志之切而乐之专也。此非无求于物者。未有能焉。今夫天下之空閒无事如余者盖少。而又其才不适世用。且欲驱之于声名禄利之场。以予夺爱恶于其间。则是非其所长。今乃释其向者之所乐而强其所短。以丧其情性之真。岂有是理也。而或者乃以此为甚清且高。不知夫无求于物者。其势易以至此。岂不谬哉。亭既成。遂次其言于壁间。以见斯亭之胜。余乐之如此。而亦欲使世人有以知是乐之易求也。
至甚切。则亦未得卒行其志而专其乐焉。惟其嗜之如好色者之见西施毛嫱。饥者之遇膏粱八珍然后。方可谓志之切而乐之专也。此非无求于物者。未有能焉。今夫天下之空閒无事如余者盖少。而又其才不适世用。且欲驱之于声名禄利之场。以予夺爱恶于其间。则是非其所长。今乃释其向者之所乐而强其所短。以丧其情性之真。岂有是理也。而或者乃以此为甚清且高。不知夫无求于物者。其势易以至此。岂不谬哉。亭既成。遂次其言于壁间。以见斯亭之胜。余乐之如此。而亦欲使世人有以知是乐之易求也。游西岳记
壬午暮春甲辰晦。既雨且晴。青霞子意欣然甚乐。将出南郭以观草木之畅茂焉。先折简以报于数三知识处。李伯温答曰。闻子有兴于南郭。岂若西岳之为美乎。是又有临望之快焉。余遂从之。诸君又复继至。敬所独未追蹑焉。于是或马或驴。或行或止。俯华谯而上。几穷其巅而暂与之息。顾视人影。日且午矣。忽有笑语隐隐。可闻于岩谷。二三子相顾而惊。披林而望焉。则有散发披衣。醉据岩岫者。时于松下。得片石而投之。二三子呀然而笑。知其为敬所也。遂与之攀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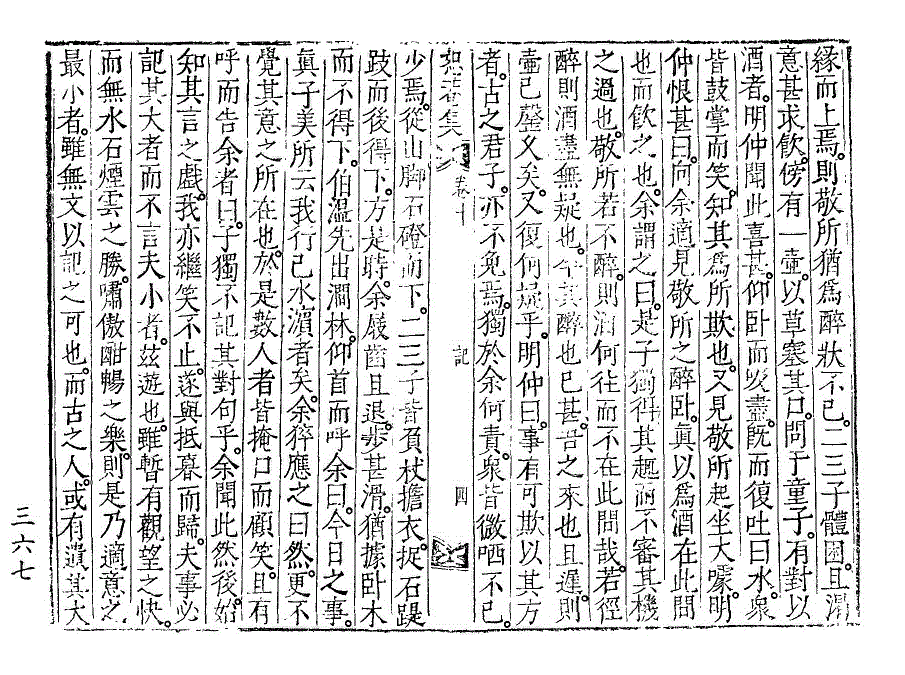 缘而上焉。则敬所犹为醉状不已。二三子体困。且渴意甚求饮。傍有一壶。以草塞其口。问于童子。有对以酒者。明仲闻此喜甚。仰卧而吸尽。既而复吐曰水。众皆鼓掌而笑。知其为所欺也。又见敬所起坐大噱。明仲恨甚曰。向余适见敬所之醉卧。真以为酒在此间也而饮之也。余谓之曰。是子独得其趣而不审其机之过也。敬所若不醉。则酒何往而不在此间哉。若径醉则酒尽无疑也。今其醉也已甚。吾之来也且迟。则壶已罄久矣。又复何疑乎。明仲曰。事有可欺以其方者。古之君子。亦不免焉。独于余何责。众皆微哂不已。少焉。从山脚石磴而下。二三子皆负杖担衣。捉石踶跂而后得下。方是时。余屐齿且退。步甚滑。犹据卧木而不得下。伯温先出涧林。仰首而呼余曰。今日之事。真子美所云我行已水滨者矣。余猝应之曰然。更不觉其意之所在也。于是数人者皆掩口而顾笑。且有呼而告余者曰。子独不记其对句乎。余闻此然后。始知其言之戏。我亦继笑不止。遂与抵暮而归。夫事必记其大者而不言夫小者。玆游也。虽暂有观望之快。而无水石烟云之胜。啸傲酣畅之乐。则是乃适意之最小者。虽无文以记之可也。而古之人。或有遗其大
缘而上焉。则敬所犹为醉状不已。二三子体困。且渴意甚求饮。傍有一壶。以草塞其口。问于童子。有对以酒者。明仲闻此喜甚。仰卧而吸尽。既而复吐曰水。众皆鼓掌而笑。知其为所欺也。又见敬所起坐大噱。明仲恨甚曰。向余适见敬所之醉卧。真以为酒在此间也而饮之也。余谓之曰。是子独得其趣而不审其机之过也。敬所若不醉。则酒何往而不在此间哉。若径醉则酒尽无疑也。今其醉也已甚。吾之来也且迟。则壶已罄久矣。又复何疑乎。明仲曰。事有可欺以其方者。古之君子。亦不免焉。独于余何责。众皆微哂不已。少焉。从山脚石磴而下。二三子皆负杖担衣。捉石踶跂而后得下。方是时。余屐齿且退。步甚滑。犹据卧木而不得下。伯温先出涧林。仰首而呼余曰。今日之事。真子美所云我行已水滨者矣。余猝应之曰然。更不觉其意之所在也。于是数人者皆掩口而顾笑。且有呼而告余者曰。子独不记其对句乎。余闻此然后。始知其言之戏。我亦继笑不止。遂与抵暮而归。夫事必记其大者而不言夫小者。玆游也。虽暂有观望之快。而无水石烟云之胜。啸傲酣畅之乐。则是乃适意之最小者。虽无文以记之可也。而古之人。或有遗其大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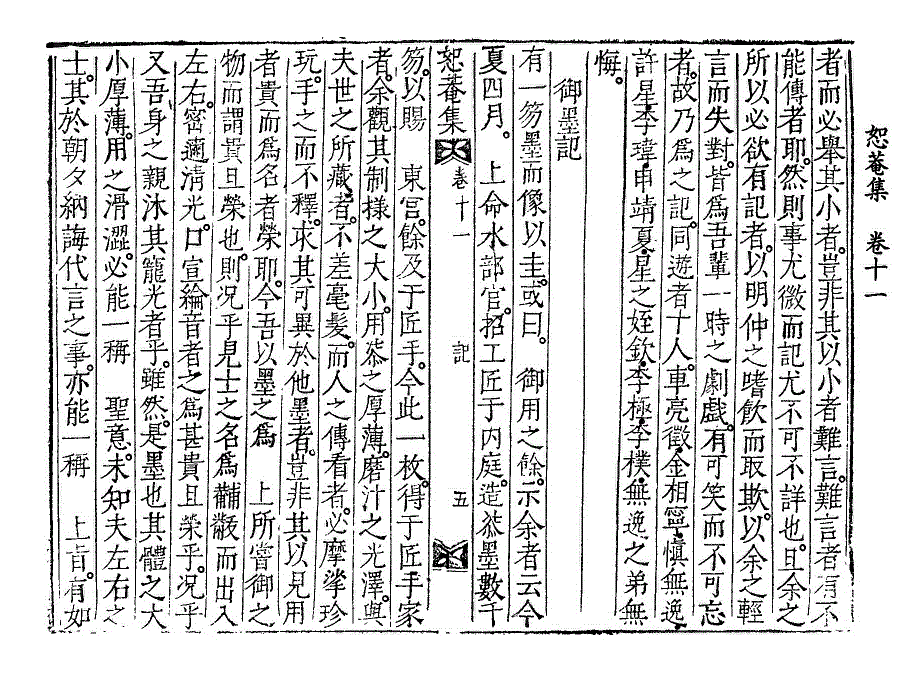 者而必举其小者。岂非其以小者难言。难言者有不能传者耶。然则事尤微而记尤不可不详也。且余之所以必欲有记者。以明仲之嗜饮而取欺。以余之轻言而失对。皆为吾辈一时之剧戏。有可笑而不可忘者。故乃为之记。同游者十人。车亮徵,金相宁,慎无逸,许星,李玮,申靖夏,星之侄钦,李极,李朴,无逸之弟无悔。
者而必举其小者。岂非其以小者难言。难言者有不能传者耶。然则事尤微而记尤不可不详也。且余之所以必欲有记者。以明仲之嗜饮而取欺。以余之轻言而失对。皆为吾辈一时之剧戏。有可笑而不可忘者。故乃为之记。同游者十人。车亮徵,金相宁,慎无逸,许星,李玮,申靖夏,星之侄钦,李极,李朴,无逸之弟无悔。御墨记
有一笏墨而像以圭。或曰。 御用之馀。示余者云今夏四月。 上命水部官。招工匠于内庭。造㓒墨数千笏。以赐 东宫。馀及于匠手。今此一枚。得于匠手家者。余观其制㨾之大小。用㓒之厚薄。磨汁之光泽。与夫世之所藏者。不差毫发。而人之传看者。必摩挲珍玩。手之而不释。求其可异于他墨者。岂非其以见用者贵而为名者荣耶。今吾以墨之为 上所尝御之物而谓贵且荣也。则况乎见士之名为黼黻而出入左右。密迩清光。口宣纶音者之为甚贵且荣乎。况乎又吾身之亲沐其宠光者乎。虽然。是墨也其体之大小厚薄。用之滑涩。必能一称 圣意。未知夫左右之士。其于朝夕纳诲代言之事。亦能一称 上旨。有如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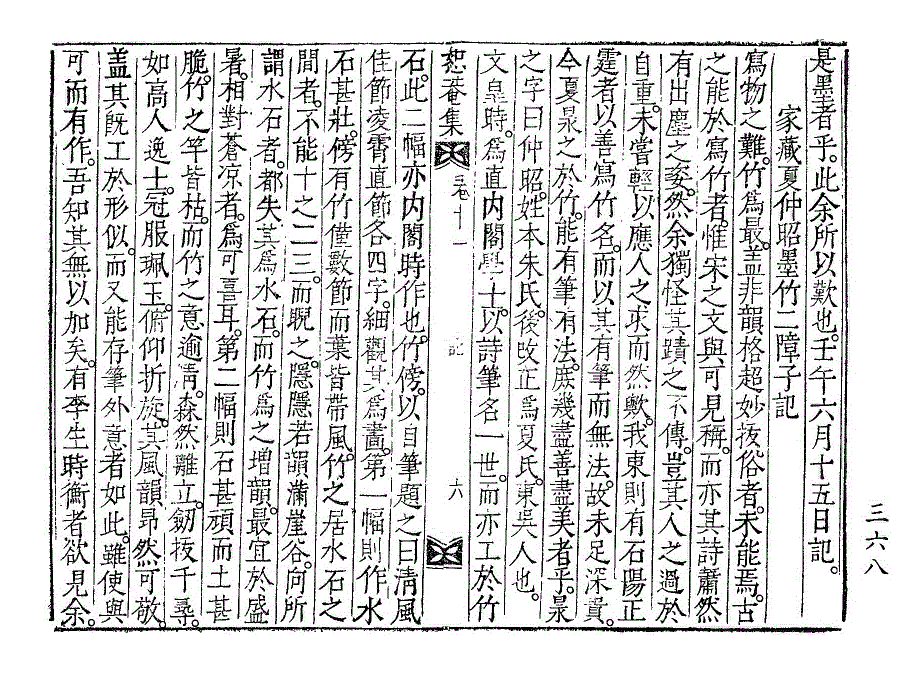 是墨者乎。此余所以叹也。壬午六月十五日记。
是墨者乎。此余所以叹也。壬午六月十五日记。家藏夏仲昭墨竹二障子记
写物之难。竹为最。盖非韵格超妙拔俗者。未能焉。古之能于写竹者。惟宋之文与可见称。而亦其诗萧然有出尘之姿。然余独怪其迹之不传。岂其人之过于自重。未尝轻以应人之求而然欤。我东则有石阳正霆者以善写竹名。而以其有笔而无法。故未足深贵。今夏昶之于竹。能有笔有法。庶几尽善尽美者乎。昶之字曰仲昭。姓本朱氏。后改正为夏氏。东吴人也。 文皇时。为直内阁学士。以诗笔名一世。而亦工于竹石。此二幅亦内阁时作也。竹傍。以自笔题之曰清风佳节凌霄直节各四字。细观其为画。第一幅则作水石甚壮。傍有竹仅数节而叶皆带风。竹之居水石之间者。不能十之二三。而睨之。隐隐若韵满崖谷。向所谓水石者。都失其为水石。而竹为之增韵。最宜于盛暑。相对苍凉者。为可喜耳。第二幅则石甚顽而土甚脆。竹之竿皆枯。而竹之意逾清。森然离立。剑拔千寻。如高人逸士。冠服佩玉。俯仰折旋。其风韵昂然可敬。盖其既工于形似。而又能存笔外意者如此。虽使与可而有作。吾知其无以加矣。有李生时衡者欲见余。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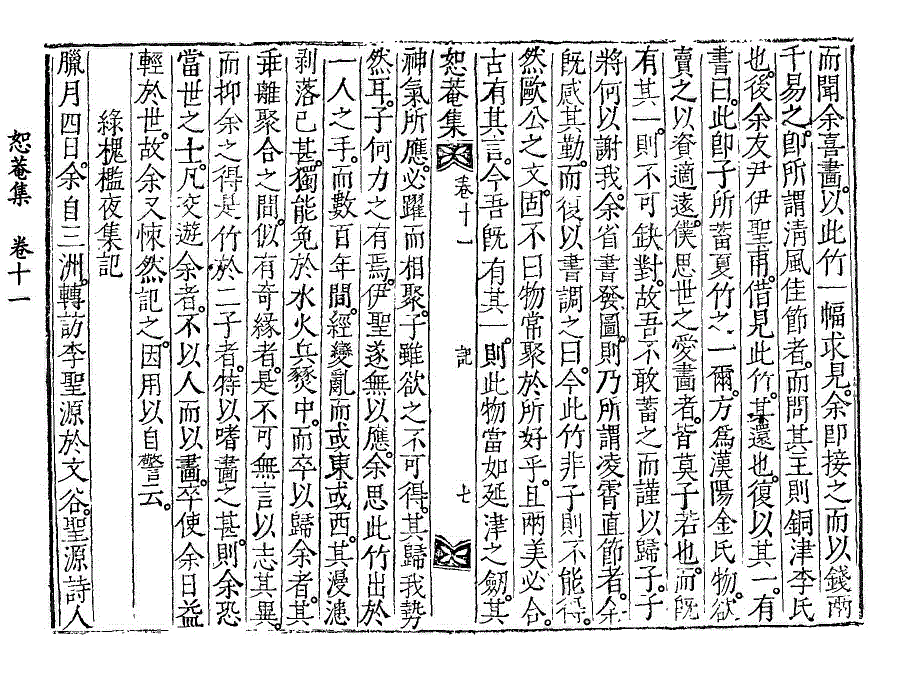 而闻余喜画。以此竹一幅求见。余即接之而以钱两千易之。即所谓清风佳节者。而问其主则铜津李氏也。后余友尹伊圣甫。借见此竹。其还也。复以其一。有书曰。此即子所蓄夏竹之一尔。方为汉阳金氏物。欲卖之以资适远。仆思世之爱画者。皆莫子若也。而既有其一。则不可缺对。故吾不敢蓄之而谨以归子。子将何以谢我。余省书发图。则乃所谓凌霄直节者。余既感其勤。而复以书调之曰。今此竹非子则不能得。然欧公之文。固不曰物常聚于所好乎。且两美必合。古有其言。今吾既有其一。则此物当如延津之剑。其神气所应。必跃而相聚。子虽欲之不可得。其归我势然耳。子何力之有焉。伊圣遂无以应。余思此竹出于一人之手。而数百年间。经变乱而或东或西。其漫漶剥落已甚。独能免于水火兵燹中。而卒以归余者。其乖离聚合之间。似有奇缘者。是不可无言以志其异。而抑余之得是竹于二子者。特以嗜画之甚。则余恐当世之士。凡交游余者。不以人而以画。卒使余日益轻于世。故余又悚然记之。因用以自警云。
而闻余喜画。以此竹一幅求见。余即接之而以钱两千易之。即所谓清风佳节者。而问其主则铜津李氏也。后余友尹伊圣甫。借见此竹。其还也。复以其一。有书曰。此即子所蓄夏竹之一尔。方为汉阳金氏物。欲卖之以资适远。仆思世之爱画者。皆莫子若也。而既有其一。则不可缺对。故吾不敢蓄之而谨以归子。子将何以谢我。余省书发图。则乃所谓凌霄直节者。余既感其勤。而复以书调之曰。今此竹非子则不能得。然欧公之文。固不曰物常聚于所好乎。且两美必合。古有其言。今吾既有其一。则此物当如延津之剑。其神气所应。必跃而相聚。子虽欲之不可得。其归我势然耳。子何力之有焉。伊圣遂无以应。余思此竹出于一人之手。而数百年间。经变乱而或东或西。其漫漶剥落已甚。独能免于水火兵燹中。而卒以归余者。其乖离聚合之间。似有奇缘者。是不可无言以志其异。而抑余之得是竹于二子者。特以嗜画之甚。则余恐当世之士。凡交游余者。不以人而以画。卒使余日益轻于世。故余又悚然记之。因用以自警云。绿槐槛夜集记
腊月四日。余自三洲。转访李圣源于文谷。圣源诗人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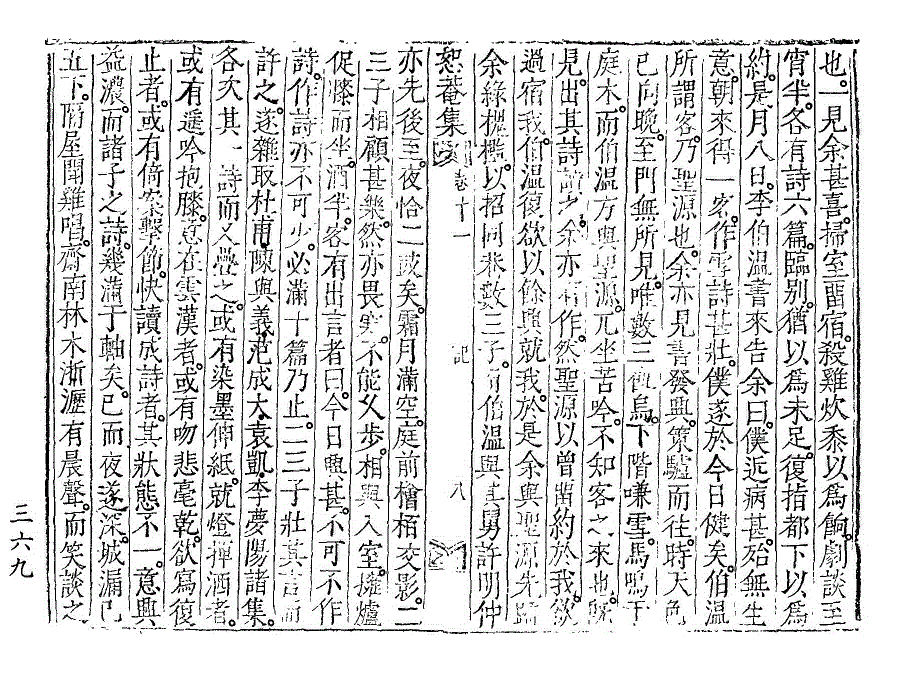 也。一见余甚喜。扫室留宿。杀鸡炊黍以为饷。剧谈至宵半。各有诗六篇。临别。犹以为未足。复指都下以为约。是月八日。李伯温书来告余曰。仆近病甚。殆无生意。朝来得一客。作雪诗甚壮。仆遂于今日健矣。伯温所谓客。乃圣源也。余亦见书发兴。策驴而往。时天色已向晚。至门无所见。唯数三饥乌。下阶嗛雪。马鸣于庭木。而伯温方与圣源。兀坐苦吟。不知客之来也。既见。出其诗读之。余亦有作。然圣源以曾留约于我。欲过宿我。伯温复欲以馀兴就我。于是余与圣源先归余绿槐槛。以招同巷数三子。而伯温与其舅许明仲亦先后至。夜恰二鼓矣。霜月满空。庭前桧柏交影。二三子相顾甚乐。然亦畏寒。不能久步。相与入室。拥炉促膝而坐。酒半。客有出言者曰。今日兴甚。不可不作诗。作诗亦不可少。必满十篇乃止。二三子壮其言而许之。遂杂取杜甫,陈与义,范成大,袁凯,李梦阳诸集。各次其一诗而又叠之。或有染墨伸纸。就灯挥洒者。或有遥吟抱膝。意在云汉者。或有吻悲毫乾。欲写复止者。或有倚案击节。快读成诗者。其状态不一。意兴益浓。而诸子之诗。几满于轴矣。已而夜遂深。城漏已五下。隔屋闻鸡唱。斋南林木淅沥有晨声。而笑谈之
也。一见余甚喜。扫室留宿。杀鸡炊黍以为饷。剧谈至宵半。各有诗六篇。临别。犹以为未足。复指都下以为约。是月八日。李伯温书来告余曰。仆近病甚。殆无生意。朝来得一客。作雪诗甚壮。仆遂于今日健矣。伯温所谓客。乃圣源也。余亦见书发兴。策驴而往。时天色已向晚。至门无所见。唯数三饥乌。下阶嗛雪。马鸣于庭木。而伯温方与圣源。兀坐苦吟。不知客之来也。既见。出其诗读之。余亦有作。然圣源以曾留约于我。欲过宿我。伯温复欲以馀兴就我。于是余与圣源先归余绿槐槛。以招同巷数三子。而伯温与其舅许明仲亦先后至。夜恰二鼓矣。霜月满空。庭前桧柏交影。二三子相顾甚乐。然亦畏寒。不能久步。相与入室。拥炉促膝而坐。酒半。客有出言者曰。今日兴甚。不可不作诗。作诗亦不可少。必满十篇乃止。二三子壮其言而许之。遂杂取杜甫,陈与义,范成大,袁凯,李梦阳诸集。各次其一诗而又叠之。或有染墨伸纸。就灯挥洒者。或有遥吟抱膝。意在云汉者。或有吻悲毫乾。欲写复止者。或有倚案击节。快读成诗者。其状态不一。意兴益浓。而诸子之诗。几满于轴矣。已而夜遂深。城漏已五下。隔屋闻鸡唱。斋南林木淅沥有晨声。而笑谈之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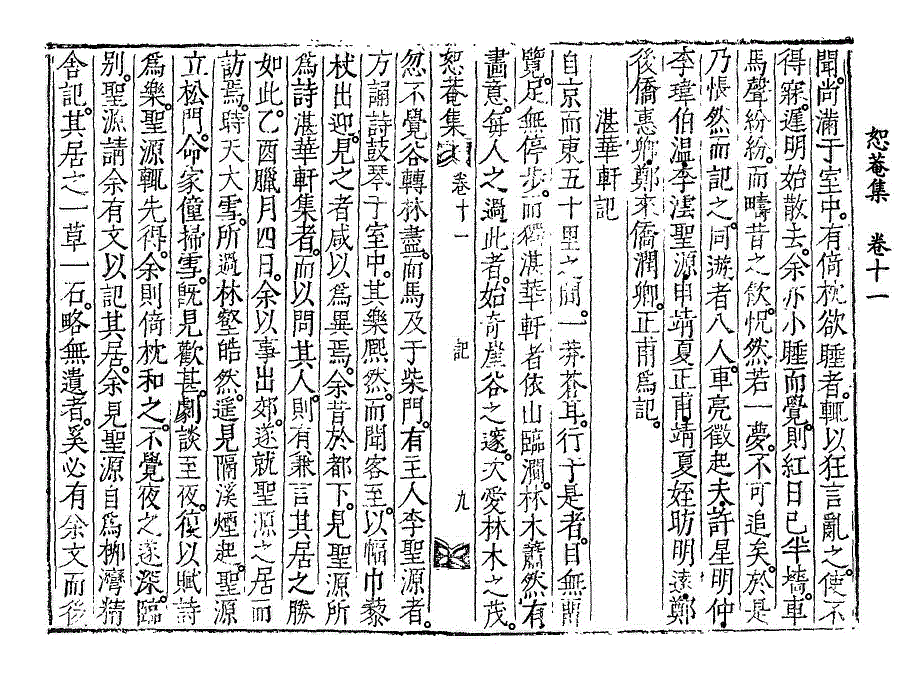 闻。尚满于室中。有倚枕欲睡者。辄以狂言乱之。使不得寐。迟明始散去。余亦小睡而觉。则红日已半墙。车马声纷纷。而畴昔之饮。恍然若一梦。不可追矣。于是乃怅然而记之。同游者八人。车亮徵起夫,许星明仲,李玮伯温,李沄圣源,申靖夏正甫,靖夏侄昉明远,郑后侨惠卿,郑来侨润卿。正甫为记。
闻。尚满于室中。有倚枕欲睡者。辄以狂言乱之。使不得寐。迟明始散去。余亦小睡而觉。则红日已半墙。车马声纷纷。而畴昔之饮。恍然若一梦。不可追矣。于是乃怅然而记之。同游者八人。车亮徵起夫,许星明仲,李玮伯温,李沄圣源,申靖夏正甫,靖夏侄昉明远,郑后侨惠卿,郑来侨润卿。正甫为记。湛华轩记
自京而东五十里之间。一莽苍耳。行于是者。目无留览。足无停步。而独湛华轩者依山临涧。林木萧然有画意。每人之过此者。始奇崖谷之邃。次爱林木之茂。忽不觉谷转林尽。而马及于柴门。有主人李圣源者。方诵诗鼓琴于室中。其乐熙然。而闻客至。以幅巾藜杖出迎。见之者咸以为异焉。余昔于都下。见圣源所为诗湛华轩集者。而以问其人。则有兼言其居之胜如此。乙酉腊月四日。余以事出郊。遂就圣源之居而访焉。时天大雪。所过林壑皓然。遥见隔溪烟起。圣源立松门。命家僮扫雪。既见欢甚。剧谈至夜。复以赋诗为乐。圣源辄先得。余则倚枕和之。不觉夜之遂深。临别。圣源请余有文以记其居。余见圣源自为柳湾精舍记。其居之一草一石。略无遗者。奚必有余文而后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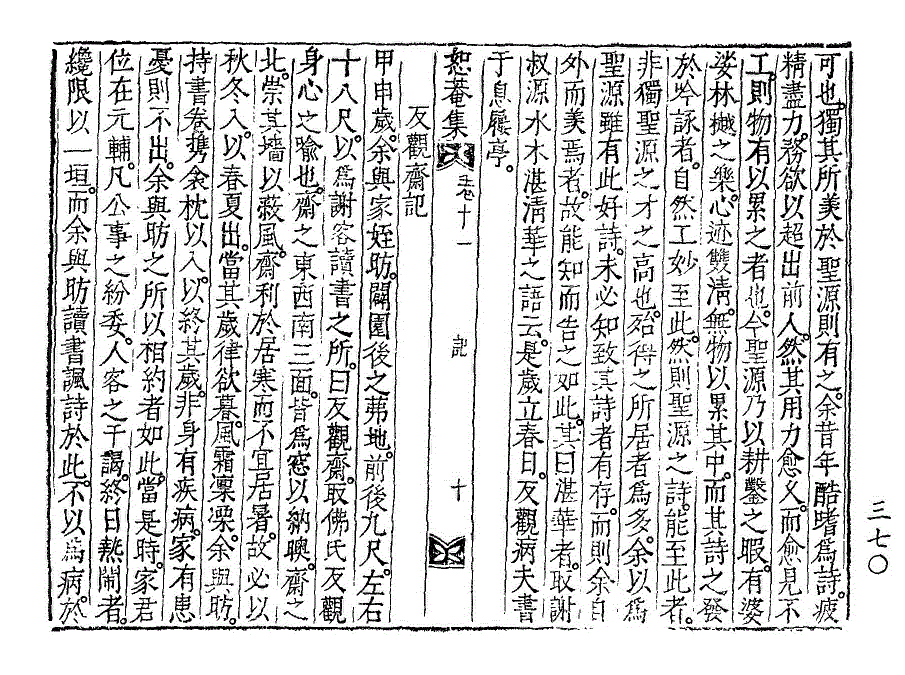 可也。独其所羡于圣源则有之。余昔年酷嗜为诗。疲精尽力。务欲以超出前人。然其用力愈久。而愈见不工。则物有以累之者也。今圣源乃以耕凿之暇。有婆娑林樾之乐。心迹双清。无物以累其中。而其诗之发于吟咏者。自然工妙至此。然则圣源之诗。能至此者。非独圣源之才之高也。殆得之所居者为多。余以为圣源虽有此好诗。未必知致其诗者有存。而则余自外而羡焉者。故能知而告之如此。其曰湛华者。取谢叔源水木湛清华之语云。是岁立春日。反观病夫书于息屦亭。
可也。独其所羡于圣源则有之。余昔年酷嗜为诗。疲精尽力。务欲以超出前人。然其用力愈久。而愈见不工。则物有以累之者也。今圣源乃以耕凿之暇。有婆娑林樾之乐。心迹双清。无物以累其中。而其诗之发于吟咏者。自然工妙至此。然则圣源之诗。能至此者。非独圣源之才之高也。殆得之所居者为多。余以为圣源虽有此好诗。未必知致其诗者有存。而则余自外而羡焉者。故能知而告之如此。其曰湛华者。取谢叔源水木湛清华之语云。是岁立春日。反观病夫书于息屦亭。反观斋记
甲申岁。余与家侄昉。辟园后之茀地。前后九尺。左右十八尺。以为谢客读书之所。曰反观斋。取佛氏反观身心之喻也。斋之东西南三面。皆为窗以纳𣋉。斋之北。崇其墙以蔽风。斋利于居寒而不宜居暑。故必以秋冬入。以春夏出。当其岁律欲暮。风霜凛凓。余与昉。持书卷携衾枕以入。以终其岁。非身有疾病。家有患忧则不出。余与昉之所以相约者如此。当是时。家君位在元辅。凡公事之纷委。人客之干谒。终日热闹者。才限以一垣。而余与昉读书讽诗于此。不以为病。于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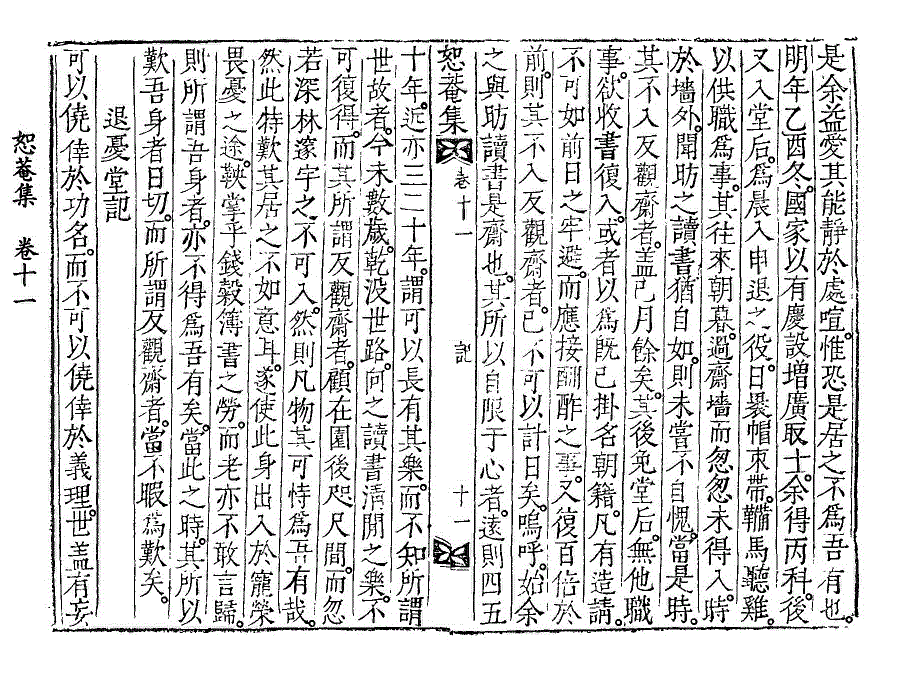 是余益爱其能静于处喧。惟恐是居之不为吾有也。明年乙酉冬。国家以有庆设增广取士。余得丙科。后又入堂后。为晨入申退之役。日裹帽束带。鞴马听鸡。以供职为事。其往来朝暮。过斋墙而匆匆未得入。时于墙外。闻昉之读书犹自如。则未尝不自愧。当是时。其不入反观斋者。盖已月馀矣。其后免堂后。无他职事。欲收书复入。或者以为既已挂名朝籍。凡有造请。不可如前日之牢避。而应接酬酢之事。又复百倍于前。则其不入反观斋者。已不可以计日矣。呜呼。始余之与昉读书是斋也。其所以自限于心者。远则四五十年。近亦三二十年。谓可以长有其乐。而不知所谓世故者。今未数岁。乾没世路。向之读书清閒之乐。不可复得。而其所谓反观斋者。顾在园后咫尺间。而忽若深林邃宇之不可入。然则凡物其可恃为吾有哉。然此特叹其居之不如意耳。遂使此身出入于宠荣畏忧之途。鞅掌乎钱谷簿书之劳。而老亦不敢言归。则所谓吾身者。亦不得为吾有矣。当此之时。其所以叹吾身者日切。而所谓反观斋者。当不暇为叹矣。
是余益爱其能静于处喧。惟恐是居之不为吾有也。明年乙酉冬。国家以有庆设增广取士。余得丙科。后又入堂后。为晨入申退之役。日裹帽束带。鞴马听鸡。以供职为事。其往来朝暮。过斋墙而匆匆未得入。时于墙外。闻昉之读书犹自如。则未尝不自愧。当是时。其不入反观斋者。盖已月馀矣。其后免堂后。无他职事。欲收书复入。或者以为既已挂名朝籍。凡有造请。不可如前日之牢避。而应接酬酢之事。又复百倍于前。则其不入反观斋者。已不可以计日矣。呜呼。始余之与昉读书是斋也。其所以自限于心者。远则四五十年。近亦三二十年。谓可以长有其乐。而不知所谓世故者。今未数岁。乾没世路。向之读书清閒之乐。不可复得。而其所谓反观斋者。顾在园后咫尺间。而忽若深林邃宇之不可入。然则凡物其可恃为吾有哉。然此特叹其居之不如意耳。遂使此身出入于宠荣畏忧之途。鞅掌乎钱谷簿书之劳。而老亦不敢言归。则所谓吾身者。亦不得为吾有矣。当此之时。其所以叹吾身者日切。而所谓反观斋者。当不暇为叹矣。退忧堂记
可以侥倖于功名。而不可以侥倖于义理。世盖有妄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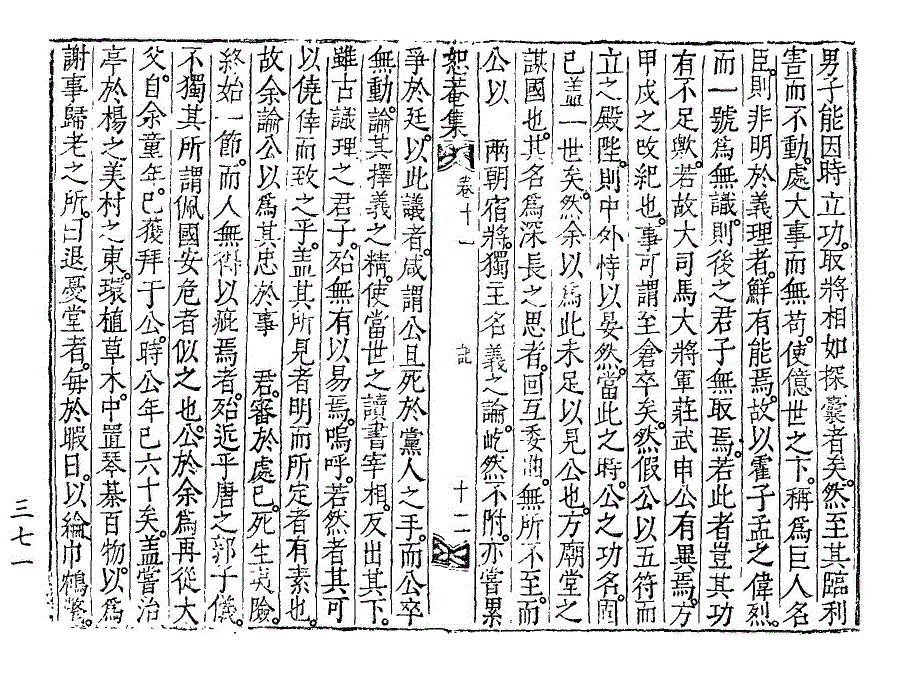 男子能因时立功。取将相如探囊者矣。然至其临利害而不动。处大事而无苟。使亿世之下。称为巨人名臣。则非明于义理者。鲜有能焉。故以霍子孟之伟烈。而一号为无识。则后之君子无取焉。若此者岂其功有不足欤。若故大司马大将军庄武申公有异焉。方甲戌之改纪也。事可谓至仓卒矣。然假公以五符而立之殿陛。则中外恃以晏然。当此之时。公之功名。固已盖一世矣。然余以为此未足以见公也。方庙堂之谋国也。其名为深长之思者。回互委曲。无所不至。而公以 两朝宿将。独主名义之论。屹然不附。亦尝累争于廷。以此议者。咸谓公且死于党人之手。而公卒无动。论其择义之精。使当世之读书宰相。反出其下。虽古识理之君子。殆无有以易焉。呜呼。若然者其可以侥倖而致之乎。盖其所见者明而所定者有素也。故余论公以为其忠于事 君。审于处己。死生夷险。终始一节。而人无得以疵焉者。殆近乎唐之郭子仪。不独其所谓佩国安危者似之也。公于余为再从大父。自余童年。已获拜于公。时公年已六十矣。盖尝治亭于杨之美村之东。环植草木。中置琴棋百物。以为谢事归老之所。曰退忧堂者。每于暇日。以纶巾鹤氅。
男子能因时立功。取将相如探囊者矣。然至其临利害而不动。处大事而无苟。使亿世之下。称为巨人名臣。则非明于义理者。鲜有能焉。故以霍子孟之伟烈。而一号为无识。则后之君子无取焉。若此者岂其功有不足欤。若故大司马大将军庄武申公有异焉。方甲戌之改纪也。事可谓至仓卒矣。然假公以五符而立之殿陛。则中外恃以晏然。当此之时。公之功名。固已盖一世矣。然余以为此未足以见公也。方庙堂之谋国也。其名为深长之思者。回互委曲。无所不至。而公以 两朝宿将。独主名义之论。屹然不附。亦尝累争于廷。以此议者。咸谓公且死于党人之手。而公卒无动。论其择义之精。使当世之读书宰相。反出其下。虽古识理之君子。殆无有以易焉。呜呼。若然者其可以侥倖而致之乎。盖其所见者明而所定者有素也。故余论公以为其忠于事 君。审于处己。死生夷险。终始一节。而人无得以疵焉者。殆近乎唐之郭子仪。不独其所谓佩国安危者似之也。公于余为再从大父。自余童年。已获拜于公。时公年已六十矣。盖尝治亭于杨之美村之东。环植草木。中置琴棋百物。以为谢事归老之所。曰退忧堂者。每于暇日。以纶巾鹤氅。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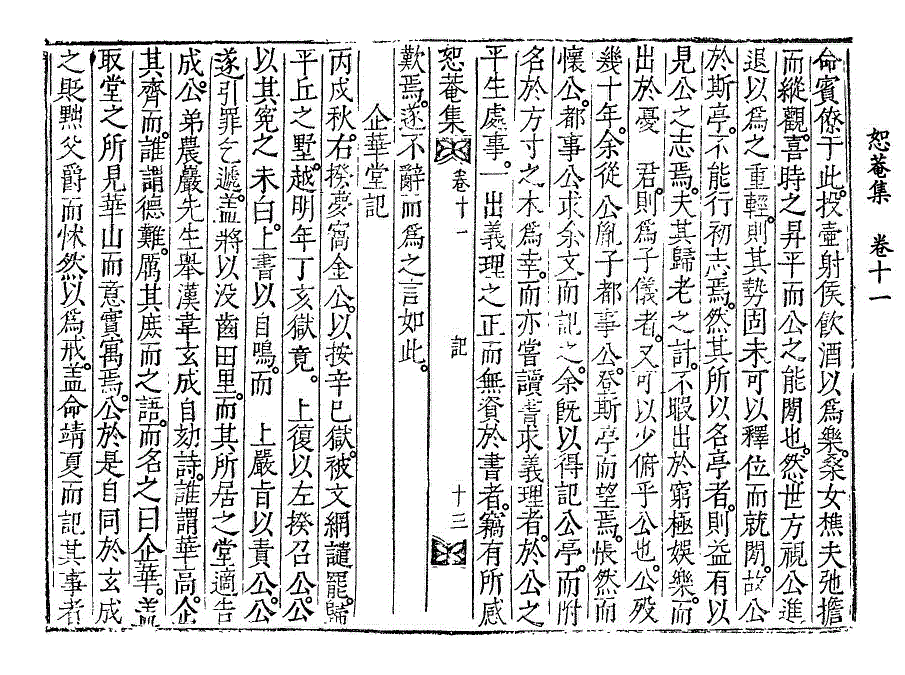 命宾僚于此。投壶射侯饮酒以为乐。桑女樵夫弛担而纵观。喜时之升平而公之能閒也。然世方视公进退以为之重轻。则其势固未可以释位而就閒。故公于斯亭。不能行初志焉。然其所以名亭者。则益有以见公之志焉。夫其归老之计。不暇出于穷极娱乐。而出于忧 君。则为子仪者。又可以少俯乎公也。公殁几十年。余从公胤子都事公。登斯亭而望焉。怅然而怀公。都事公求余文而记之。余既以得记公亭。而附名于方寸之木为幸。而亦尝读书求义理者。于公之平生处事。一出义理之正而无资于书者。窃有所感叹焉。遂不辞而为之言如此。
命宾僚于此。投壶射侯饮酒以为乐。桑女樵夫弛担而纵观。喜时之升平而公之能閒也。然世方视公进退以为之重轻。则其势固未可以释位而就閒。故公于斯亭。不能行初志焉。然其所以名亭者。则益有以见公之志焉。夫其归老之计。不暇出于穷极娱乐。而出于忧 君。则为子仪者。又可以少俯乎公也。公殁几十年。余从公胤子都事公。登斯亭而望焉。怅然而怀公。都事公求余文而记之。余既以得记公亭。而附名于方寸之木为幸。而亦尝读书求义理者。于公之平生处事。一出义理之正而无资于书者。窃有所感叹焉。遂不辞而为之言如此。企华堂记
丙戌秋。右揆梦窝金公。以按辛巳狱。被文网谴罢。归平丘之墅。越明年丁亥狱竟。 上复以左揆召公。公以其冤之未白。上书以自鸣。而 上严旨以责公。公遂引罪乞递。盖将以没齿田里。而其所居之堂适告成。公弟农岩先生举汉韦玄成自劾诗。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庶而之语。而名之曰企华。盖取堂之所见华山而意实寓焉。公于是自同于玄成之贬黜父爵而怵然以为戒。盖命靖夏而记其事者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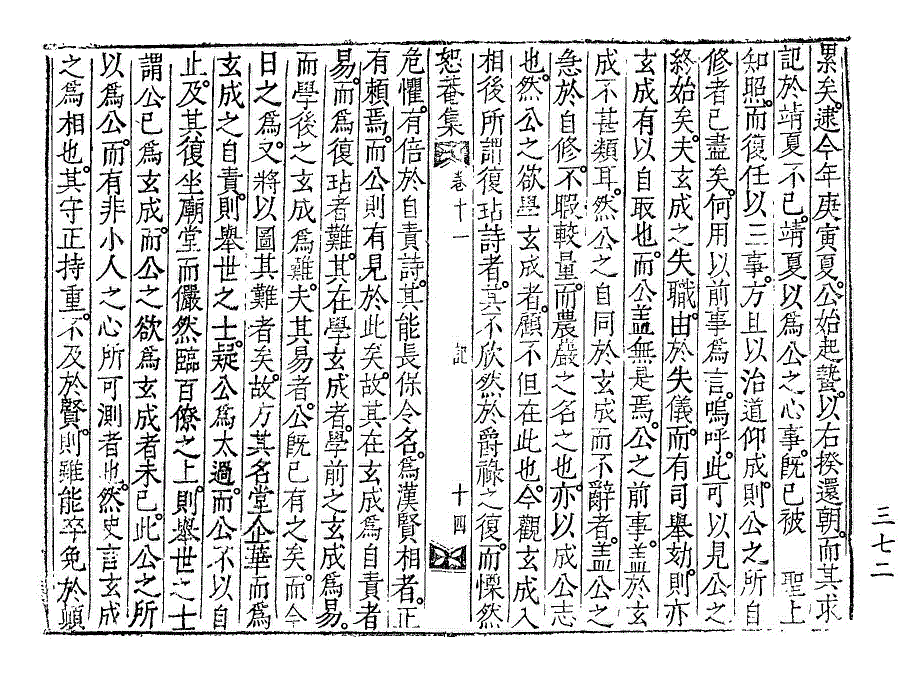 累矣。逮今年庚寅夏。公始起蛰。以右揆还朝。而其求记于靖夏不已。靖夏以为公之心事。既已被 圣上知照。而复任以三事。方且以治道仰成。则公之所自修者已尽矣。何用以前事为言。呜呼。此可以见公之终始矣。夫玄成之失职。由于失仪。而有司举劾。则亦玄成有以自取也。而公盖无是焉。公之前事。盖于玄成不甚类耳。然公之自同于玄成而不辞者。盖公之急于自修。不暇较量。而农岩之名之也。亦以成公志也。然公之欲学玄成者。顾不但在此也。今观玄成入相后所谓复玷诗者。其不欣然于爵禄之复。而慄然危惧。有倍于自责诗。其能长保令名。为汉贤相者。正有赖焉。而公则有见于此矣。故其在玄成为自责者易。而为复玷者难。其在学玄成者。学前之玄成为易。而学后之玄成为难。夫其易者。公既已有之矣。而今日之为。又将以图其难者矣。故方其名堂企华而为玄成之自责。则举世之士。疑公为太过。而公不以自止。及其复坐庙堂而俨然临百僚之上。则举世之士谓公已为玄成。而公之欲为玄成者未已。此公之所以为公。而有非小人之心所可测者也。然史言玄成之为相也。其守正持重。不及于贤。则虽能卒免于颠
累矣。逮今年庚寅夏。公始起蛰。以右揆还朝。而其求记于靖夏不已。靖夏以为公之心事。既已被 圣上知照。而复任以三事。方且以治道仰成。则公之所自修者已尽矣。何用以前事为言。呜呼。此可以见公之终始矣。夫玄成之失职。由于失仪。而有司举劾。则亦玄成有以自取也。而公盖无是焉。公之前事。盖于玄成不甚类耳。然公之自同于玄成而不辞者。盖公之急于自修。不暇较量。而农岩之名之也。亦以成公志也。然公之欲学玄成者。顾不但在此也。今观玄成入相后所谓复玷诗者。其不欣然于爵禄之复。而慄然危惧。有倍于自责诗。其能长保令名。为汉贤相者。正有赖焉。而公则有见于此矣。故其在玄成为自责者易。而为复玷者难。其在学玄成者。学前之玄成为易。而学后之玄成为难。夫其易者。公既已有之矣。而今日之为。又将以图其难者矣。故方其名堂企华而为玄成之自责。则举世之士。疑公为太过。而公不以自止。及其复坐庙堂而俨然临百僚之上。则举世之士谓公已为玄成。而公之欲为玄成者未已。此公之所以为公。而有非小人之心所可测者也。然史言玄成之为相也。其守正持重。不及于贤。则虽能卒免于颠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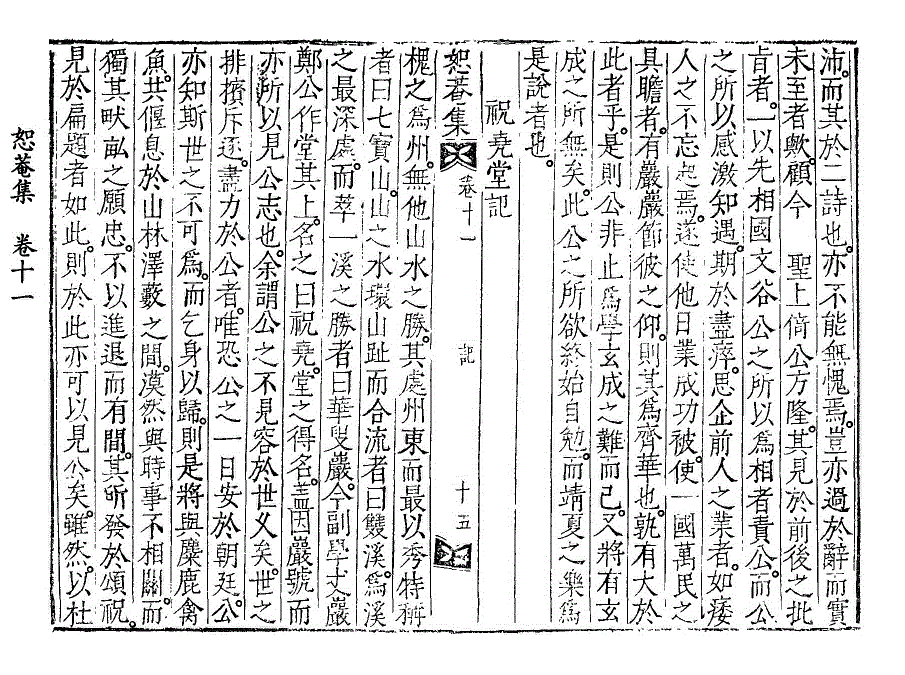 沛。而其于二诗也。亦不能无愧焉。岂亦过于辞而实未至者欤。顾今 圣上倚公方隆。其见于前后之批旨者。一以先相国文谷公之所以为相者责公。而公之所以感激知遇。期于尽瘁。思企前人之业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焉。遂使他日业成功被。使一国万民之具瞻者。有岩岩节彼之仰。则其为齐华也。孰有大于此者乎。是则公非止为学玄成之难而已。又将有玄成之所无矣。此公之所欲终始自勉。而靖夏之乐为是说者也。
沛。而其于二诗也。亦不能无愧焉。岂亦过于辞而实未至者欤。顾今 圣上倚公方隆。其见于前后之批旨者。一以先相国文谷公之所以为相者责公。而公之所以感激知遇。期于尽瘁。思企前人之业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焉。遂使他日业成功被。使一国万民之具瞻者。有岩岩节彼之仰。则其为齐华也。孰有大于此者乎。是则公非止为学玄成之难而已。又将有玄成之所无矣。此公之所欲终始自勉。而靖夏之乐为是说者也。祝尧堂记
槐之为州。无他山水之胜。其处州东而最以秀特称者曰七宝山。山之水环山趾而合流者曰双溪。为溪之最深处。而萃一溪之胜者曰华叟岩。今副学丈岩郑公作堂其上。名之曰祝尧。堂之得名。盖因岩号而亦所以见公志也。余谓公之不见容于世久矣。世之排摈斥逐。尽力于公者。唯恐公之一日安于朝廷。公亦知斯世之不可为。而乞身以归。则是将与麋鹿禽鱼。共偃息于山林泽薮之间。漠然与时事不相关。而独其畎亩之愿忠。不以进退而有间。其所发于颂祝。见于扁题者如此。则于此亦可以见公矣。虽然。以杜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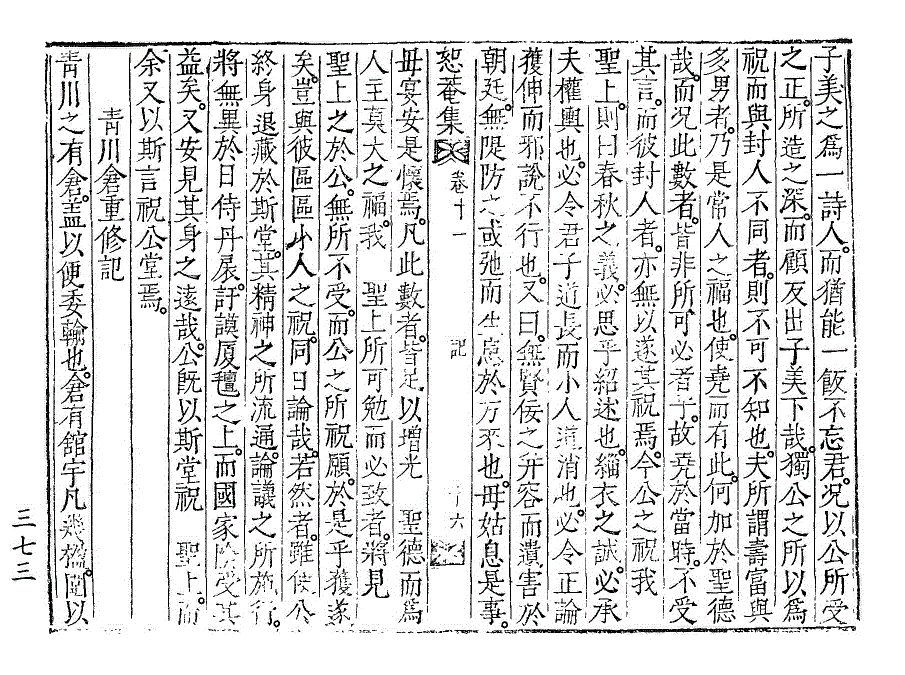 子美之为一诗人。而犹能一饭不忘君。况以公所受之正。所造之深。而顾反出子美下哉。独公之所以为祝而与封人不同者。则不可不知也。夫所谓寿富与多男者。乃是常人之福也。使尧而有此。何加于圣德哉。而况此数者。皆非所可必者乎。故尧于当时。不受其言。而彼封人者。亦无以遂其祝焉。今公之祝我 圣上。则曰春秋之义。必思乎绍述也。缁衣之诚。必承夫权舆也。必令君子道长而小人道消也。必令正论获伸而邪说不行也。又曰。无贤佞之并容而遗害于朝廷。无堤防之或弛而生患于方来也。毋姑息是事。毋宴安是怀焉。凡此数者。皆足以增光 圣德而为人主莫大之福。我 圣上所可勉而必致者。将见 圣上之于公。无所不受。而公之所祝愿。于是乎获遂矣。岂与彼区区小人之祝。同日论哉。若然者。虽使公终身退藏于斯堂。其精神之所流通。论议之所施行。将无异于日侍丹扆。吁谟厦毡之上。而国家阴受其益矣。又安见其身之远哉。公既以斯堂祝 圣上。而余又以斯言祝公堂焉。
子美之为一诗人。而犹能一饭不忘君。况以公所受之正。所造之深。而顾反出子美下哉。独公之所以为祝而与封人不同者。则不可不知也。夫所谓寿富与多男者。乃是常人之福也。使尧而有此。何加于圣德哉。而况此数者。皆非所可必者乎。故尧于当时。不受其言。而彼封人者。亦无以遂其祝焉。今公之祝我 圣上。则曰春秋之义。必思乎绍述也。缁衣之诚。必承夫权舆也。必令君子道长而小人道消也。必令正论获伸而邪说不行也。又曰。无贤佞之并容而遗害于朝廷。无堤防之或弛而生患于方来也。毋姑息是事。毋宴安是怀焉。凡此数者。皆足以增光 圣德而为人主莫大之福。我 圣上所可勉而必致者。将见 圣上之于公。无所不受。而公之所祝愿。于是乎获遂矣。岂与彼区区小人之祝。同日论哉。若然者。虽使公终身退藏于斯堂。其精神之所流通。论议之所施行。将无异于日侍丹扆。吁谟厦毡之上。而国家阴受其益矣。又安见其身之远哉。公既以斯堂祝 圣上。而余又以斯言祝公堂焉。青川仓重修记
青川之有仓。盖以便委输也。仓有馆宇凡几楹。围以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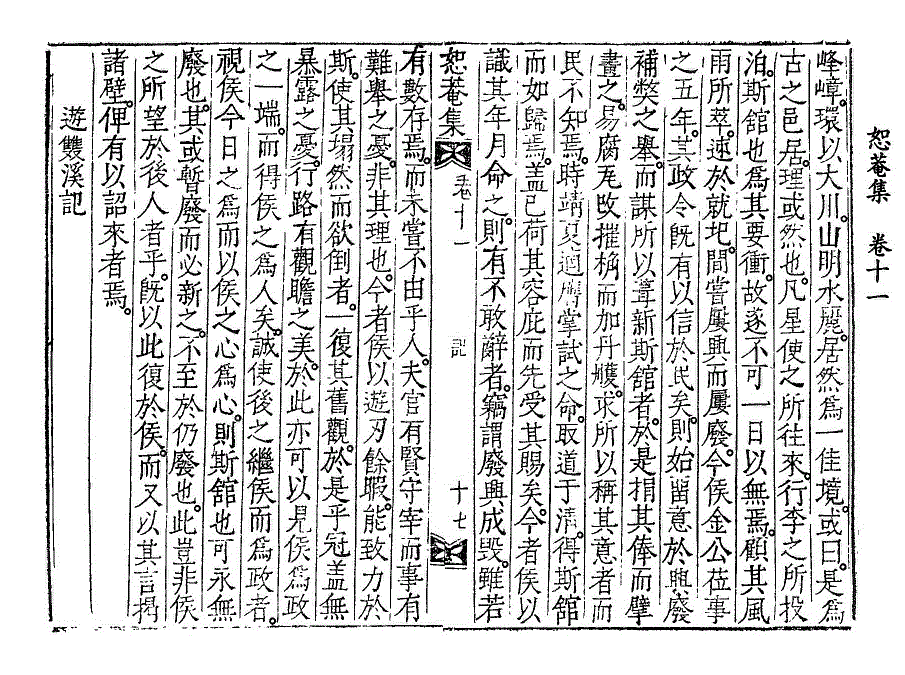 峰嶂。环以大川。山明水丽。居然为一佳境。或曰。是为古之邑居。理或然也。凡星使之所往来。行李之所投泊。斯馆也为其要冲。故遂不可一日以无焉。顾其风雨所萃。速于就圮。间尝屡兴而屡废。今侯金公莅事之五年。其政令既有以信于民矣。则始留意于兴废补弊之举。而谋所以葺新斯馆者。于是捐其俸而擘画之。易腐瓦改摧桷而加丹雘。求所以称其意者而民不知焉。时靖夏适膺掌试之命。取道于清。得斯馆而如归焉。盖已荷其容庇而先受其赐矣。今者侯以识其年月命之。则有不敢辞者。窃谓废兴成毁。虽若有数存焉。而未尝不由乎人。夫官有贤守宰而事有难举之忧。非其理也。今者侯以游刃馀暇。能致力于斯。使其塌然而欲倒者。一复其旧观。于是乎冠盖无暴露之忧。行路有观瞻之美。于此亦可以见侯为政之一端。而得侯之为人矣。诚使后之继侯而为政者。视侯今日之为而以侯之心为心。则斯馆也可永无废也。其或暂废而必新之。不至于仍废也。此岂非侯之所望于后人者乎。既以此复于侯。而又以其言揭诸壁。俾有以诏来者焉。
峰嶂。环以大川。山明水丽。居然为一佳境。或曰。是为古之邑居。理或然也。凡星使之所往来。行李之所投泊。斯馆也为其要冲。故遂不可一日以无焉。顾其风雨所萃。速于就圮。间尝屡兴而屡废。今侯金公莅事之五年。其政令既有以信于民矣。则始留意于兴废补弊之举。而谋所以葺新斯馆者。于是捐其俸而擘画之。易腐瓦改摧桷而加丹雘。求所以称其意者而民不知焉。时靖夏适膺掌试之命。取道于清。得斯馆而如归焉。盖已荷其容庇而先受其赐矣。今者侯以识其年月命之。则有不敢辞者。窃谓废兴成毁。虽若有数存焉。而未尝不由乎人。夫官有贤守宰而事有难举之忧。非其理也。今者侯以游刃馀暇。能致力于斯。使其塌然而欲倒者。一复其旧观。于是乎冠盖无暴露之忧。行路有观瞻之美。于此亦可以见侯为政之一端。而得侯之为人矣。诚使后之继侯而为政者。视侯今日之为而以侯之心为心。则斯馆也可永无废也。其或暂废而必新之。不至于仍废也。此岂非侯之所望于后人者乎。既以此复于侯。而又以其言揭诸壁。俾有以诏来者焉。游双溪记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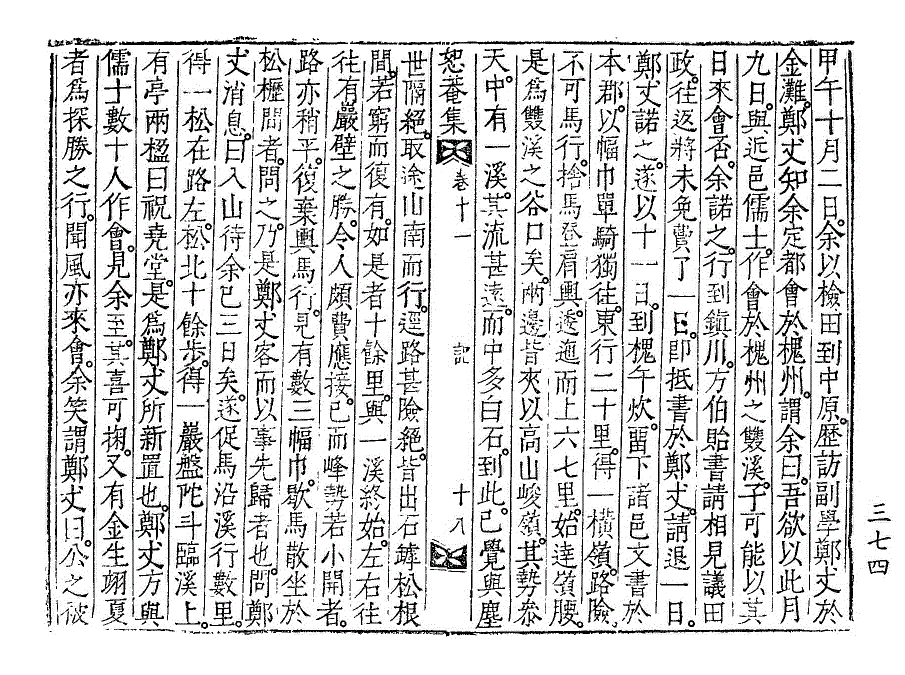 甲午十月二日。余以检田到中原。历访副学郑丈于金滩。郑丈知余定都会于槐州。谓余曰。吾欲以此月九日。与近邑儒士。作会于槐州之双溪。子可能以其日来会否。余诺之。行到镇川。方伯贻书请相见议田政。往返将未免费了一日。即抵书于郑丈。请退一日。郑丈诺之。遂以十一日。到槐午炊。留下诸邑文书于本郡。以幅巾单骑独往。东行二十里。得一横岭。路险。不可马行。舍马登肩舆。逶迤而上六七里。始达岭腰。是为双溪之谷口矣。两边皆夹以高山峻岭。其势参天。中有一溪。其流甚远。而中多白石。到此。已觉与尘世隔绝。取途山南而行。径路甚险绝。皆出石罅松根间。若穷而复有。如是者十馀里。与一溪终始。左右往往有岩壁之胜。令人颇费应接。已而峰势若小开者。路亦稍平。复弃舆马行。见有数三幅巾。歇马散坐于松枥间者。问之。乃是郑丈客而以事先归者也。问郑丈消息。曰入山待余已三日矣。遂促马沿溪行数里。得一松在路左。松北十馀步。得一岩盘陀斗临溪上。有亭两楹曰祝尧堂。是为郑丈所新置也。郑丈方与儒士数十人作会。见余至。其喜可掬。又有金生翊夏者为探胜之行。闻风亦来会。余笑谓郑丈曰。公之被
甲午十月二日。余以检田到中原。历访副学郑丈于金滩。郑丈知余定都会于槐州。谓余曰。吾欲以此月九日。与近邑儒士。作会于槐州之双溪。子可能以其日来会否。余诺之。行到镇川。方伯贻书请相见议田政。往返将未免费了一日。即抵书于郑丈。请退一日。郑丈诺之。遂以十一日。到槐午炊。留下诸邑文书于本郡。以幅巾单骑独往。东行二十里。得一横岭。路险。不可马行。舍马登肩舆。逶迤而上六七里。始达岭腰。是为双溪之谷口矣。两边皆夹以高山峻岭。其势参天。中有一溪。其流甚远。而中多白石。到此。已觉与尘世隔绝。取途山南而行。径路甚险绝。皆出石罅松根间。若穷而复有。如是者十馀里。与一溪终始。左右往往有岩壁之胜。令人颇费应接。已而峰势若小开者。路亦稍平。复弃舆马行。见有数三幅巾。歇马散坐于松枥间者。问之。乃是郑丈客而以事先归者也。问郑丈消息。曰入山待余已三日矣。遂促马沿溪行数里。得一松在路左。松北十馀步。得一岩盘陀斗临溪上。有亭两楹曰祝尧堂。是为郑丈所新置也。郑丈方与儒士数十人作会。见余至。其喜可掬。又有金生翊夏者为探胜之行。闻风亦来会。余笑谓郑丈曰。公之被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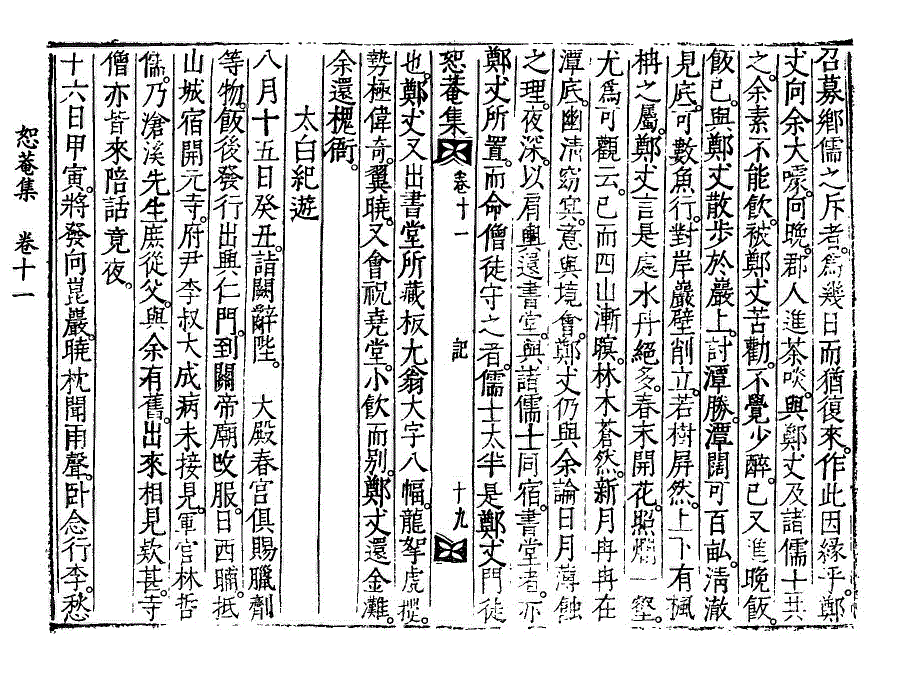 召募乡儒之斥者。为几日而犹复来。作此因缘乎。郑丈向余大噱。向晚。郡人进茶啖。与郑丈及诸儒士共之。余素不能饮。被郑丈苦劝。不觉少醉。已又进晚饭。饭已。与郑丈散步于岩上。讨潭胜。潭阔可百亩。清澈见底。可数鱼行。对岸岩壁削立。若树屏然。上下有枫楠之属。郑丈言是处水丹绝多。春末开花。照烂一壑。尤为可观云。已而四山渐暝。林木苍然。新月冉冉在潭底。幽清窈冥。意与境会。郑丈仍与余论日月薄蚀之理。夜深。以肩舆还书堂。与诸儒士同宿。书堂者。亦郑丈所置。而命僧徒守之者。儒士太半是郑丈门徒也。郑丈又出书堂所藏板尤翁大字八幅。龙挐虎攫。势极伟奇。翼晓。又会祝尧堂。小饮而别。郑丈还金滩。余还槐衙。
召募乡儒之斥者。为几日而犹复来。作此因缘乎。郑丈向余大噱。向晚。郡人进茶啖。与郑丈及诸儒士共之。余素不能饮。被郑丈苦劝。不觉少醉。已又进晚饭。饭已。与郑丈散步于岩上。讨潭胜。潭阔可百亩。清澈见底。可数鱼行。对岸岩壁削立。若树屏然。上下有枫楠之属。郑丈言是处水丹绝多。春末开花。照烂一壑。尤为可观云。已而四山渐暝。林木苍然。新月冉冉在潭底。幽清窈冥。意与境会。郑丈仍与余论日月薄蚀之理。夜深。以肩舆还书堂。与诸儒士同宿。书堂者。亦郑丈所置。而命僧徒守之者。儒士太半是郑丈门徒也。郑丈又出书堂所藏板尤翁大字八幅。龙挐虎攫。势极伟奇。翼晓。又会祝尧堂。小饮而别。郑丈还金滩。余还槐衙。太白纪游
八月十五日癸丑。诣阙辞陛。 大殿春宫俱赐腊剂等物。饭后发行出兴仁门。到关帝庙改服。日西晡。抵山城宿开元寺。府尹李叔大成病未接见。军官林哲儒。乃沧溪先生庶从父。与余有旧。出来相见款甚。寺僧亦皆来陪话竟夜。
十六日甲寅。将发向昆岩。晓枕闻雨声。卧念行李。愁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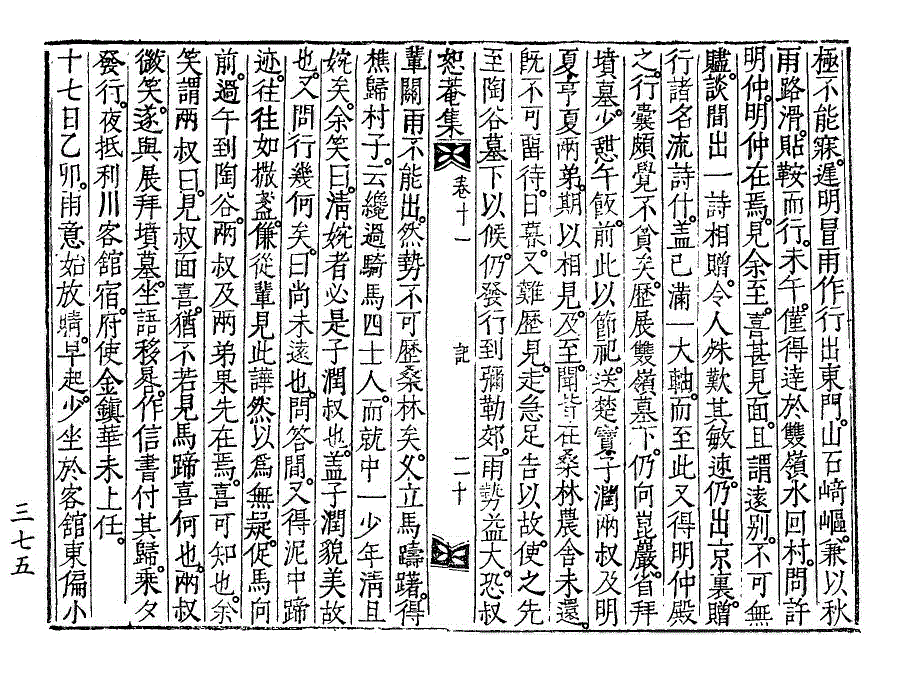 极不能寐。迟明冒雨作行出东门。山石崎岖。兼以秋雨路滑。贴鞍而行。未午。仅得达于双岭水回村。问许明仲。明仲在焉。见余至。喜甚见面。且谓远别。不可无赆。谈间出一诗相赠。令人殊叹其敏速。仍出京里。赠行诸名流诗什。盖已满一大轴。而至此又得明仲殿之。行囊颇觉不贫矣。历展双岭墓下。仍向昆岩。省拜坟墓。少憩午饭。前此以节祀。送楚宝,子润两叔及明夏,亨夏两弟。期以相见。及至。闻皆在桑林农舍未还。既不可留待。日暮。又难历见。走急足告以故。使之先至陶谷墓下以候。仍发行到弥勒郊。雨势益大。恐叔辈关雨不能出。然势不可历桑林矣。久立马踌躇。得樵归村子。云才过骑马四士人。而就中一少年清且婉矣。余笑曰。清婉者必是子润叔也。盖子润貌美故也。又问行几何矣。曰尚未远也。问答间。又得泥中蹄迹。往往如撒盏。傔从辈见此哗然以为无疑。促马向前。过午到陶谷。两叔及两弟果先在焉。喜可知也。余笑谓两叔曰。见叔面喜。犹不若见马蹄喜何也。两叔微笑。遂与展拜坟墓。坐语移晷。作信书付其归。乘夕发行。夜抵利川客馆宿。府使金镇华未上任。
极不能寐。迟明冒雨作行出东门。山石崎岖。兼以秋雨路滑。贴鞍而行。未午。仅得达于双岭水回村。问许明仲。明仲在焉。见余至。喜甚见面。且谓远别。不可无赆。谈间出一诗相赠。令人殊叹其敏速。仍出京里。赠行诸名流诗什。盖已满一大轴。而至此又得明仲殿之。行囊颇觉不贫矣。历展双岭墓下。仍向昆岩。省拜坟墓。少憩午饭。前此以节祀。送楚宝,子润两叔及明夏,亨夏两弟。期以相见。及至。闻皆在桑林农舍未还。既不可留待。日暮。又难历见。走急足告以故。使之先至陶谷墓下以候。仍发行到弥勒郊。雨势益大。恐叔辈关雨不能出。然势不可历桑林矣。久立马踌躇。得樵归村子。云才过骑马四士人。而就中一少年清且婉矣。余笑曰。清婉者必是子润叔也。盖子润貌美故也。又问行几何矣。曰尚未远也。问答间。又得泥中蹄迹。往往如撒盏。傔从辈见此哗然以为无疑。促马向前。过午到陶谷。两叔及两弟果先在焉。喜可知也。余笑谓两叔曰。见叔面喜。犹不若见马蹄喜何也。两叔微笑。遂与展拜坟墓。坐语移晷。作信书付其归。乘夕发行。夜抵利川客馆宿。府使金镇华未上任。十七日乙卯。雨意始放晴。早起。少坐于客馆东偏小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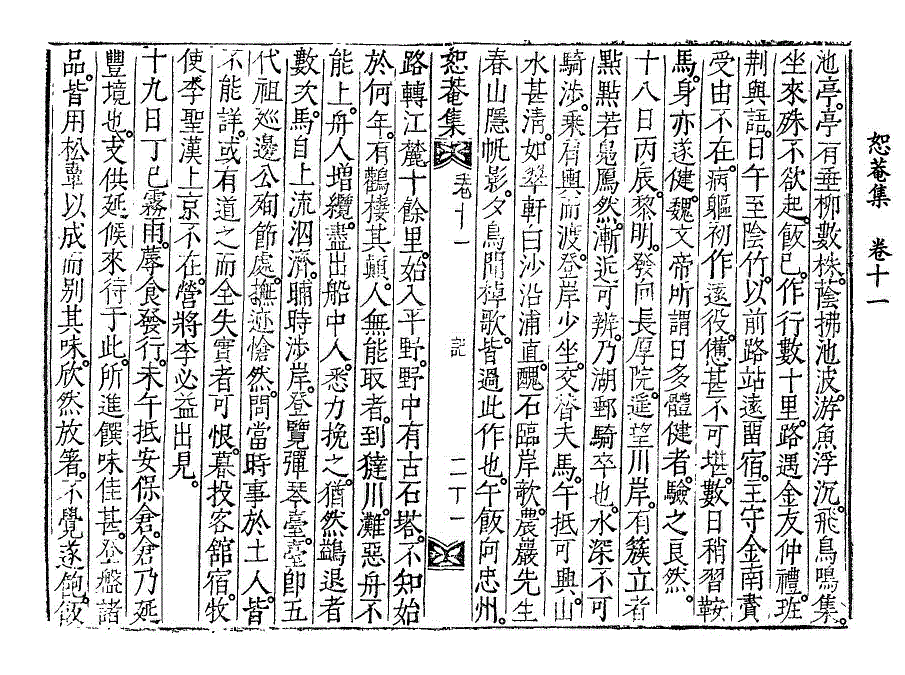 池亭。亭有垂柳数株。荫拂池波。游鱼浮沉。飞鸟鸣集。坐来殊不欲起。饭已。作行数十里。路遇金友仲礼。班荆与语。日午至阴竹。以前路站远留宿。主守金南赆受由不在。病躯初作远役。惫甚不可堪。数日稍习鞍马。身亦遂健。魏文帝所谓日多体健者。验之良然。
池亭。亭有垂柳数株。荫拂池波。游鱼浮沉。飞鸟鸣集。坐来殊不欲起。饭已。作行数十里。路遇金友仲礼。班荆与语。日午至阴竹。以前路站远留宿。主守金南赆受由不在。病躯初作远役。惫甚不可堪。数日稍习鞍马。身亦遂健。魏文帝所谓日多体健者。验之良然。十八日丙辰。黎明。发向长厚院。遥望川岸。有簇立者点点若凫雁然。渐近可辨。乃湖邮骑卒也。水深不可骑涉。乘肩舆而渡。登岸少坐。交替夫马。午抵可兴。山水甚清。如翠轩白沙沿浦直。丑石临岸欹。农岩先生春山隐帆影。夕鸟闻棹歌。皆过此作也。午饭向忠州。路转江麓十馀里。始入平野。野中有古石塔。不知始于何年。有鹳栖其颠。人无能取者。到獭川。滩恶舟不能上。舟人增缆。尽出船中人。悉力挽之。犹然鹢退者数次。马自上流泅济。晡时涉岸。登览弹琴台。台即五代祖巡边公殉节处。抚迹怆然。问当时事于土人。皆不能详。或有道之而全失实者可恨。暮投客馆宿。牧使李圣汉上京不在。营将李必益出见。
十九日丁巳雾雨。蓐食发行。未午抵安保仓。仓乃延丰境也。支供延候来待于此。所进馔味佳甚。登盘诸品。皆用松蕈以成而别其味。欣然放箸。不觉遂饱。饭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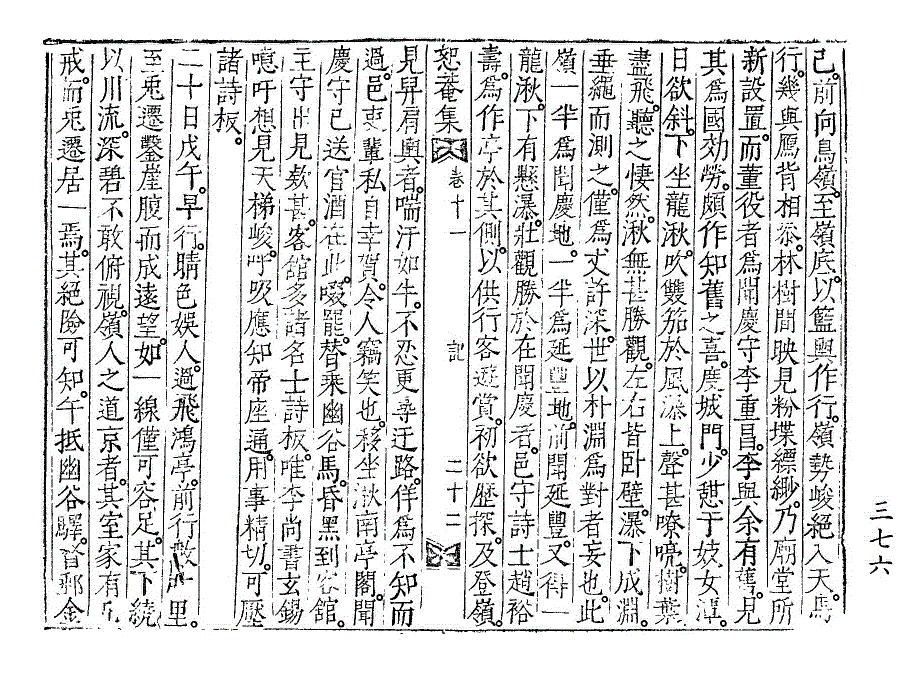 已。前向鸟岭。至岭底。以篮舆作行。岭势峻绝入天。马行。几与雁背相参。林树间映见粉堞缥缈。乃庙堂所新设置。而董役者为闻庆守李重昌。李与余有旧。见其为国效劳。颇作知旧之喜。度城门。少憩于妓女潭。日欲斜。下坐龙湫。吹双笳于风瀑上。声甚嘹喨。树叶尽飞。听之悽然。湫无甚胜观。左右皆卧壁。瀑下成渊。垂绳而测之。仅为丈许深。世以朴渊为对者妄也。此岭一半为闻庆地。一半为延丰地。前闻延丰。又得一龙湫。下有悬瀑。壮观胜于在闻庆者。邑守诗士赵裕寿。为作亭于其侧。以供行客游赏。初欲历探。及登岭。见舁肩舆者。喘汗如牛。不忍更寻迂路。佯为不知而过。邑吏辈私自幸贺。令人窃笑也。移坐湫南亭阁。闻庆守已送官酒在此。啜罢。替乘幽谷马。昏黑到客馆。主守出见款甚。客馆多诸名士诗板。唯李尚书玄锡噫吁想见天梯峻。呼吸应知帝座通。用事精切。可压诸诗板。
已。前向鸟岭。至岭底。以篮舆作行。岭势峻绝入天。马行。几与雁背相参。林树间映见粉堞缥缈。乃庙堂所新设置。而董役者为闻庆守李重昌。李与余有旧。见其为国效劳。颇作知旧之喜。度城门。少憩于妓女潭。日欲斜。下坐龙湫。吹双笳于风瀑上。声甚嘹喨。树叶尽飞。听之悽然。湫无甚胜观。左右皆卧壁。瀑下成渊。垂绳而测之。仅为丈许深。世以朴渊为对者妄也。此岭一半为闻庆地。一半为延丰地。前闻延丰。又得一龙湫。下有悬瀑。壮观胜于在闻庆者。邑守诗士赵裕寿。为作亭于其侧。以供行客游赏。初欲历探。及登岭。见舁肩舆者。喘汗如牛。不忍更寻迂路。佯为不知而过。邑吏辈私自幸贺。令人窃笑也。移坐湫南亭阁。闻庆守已送官酒在此。啜罢。替乘幽谷马。昏黑到客馆。主守出见款甚。客馆多诸名士诗板。唯李尚书玄锡噫吁想见天梯峻。呼吸应知帝座通。用事精切。可压诸诗板。二十日戊午。早行。晴色娱人。过飞鸿亭。前行数十里。至兔迁凿崖腹而成远望。如一线仅可容足。其下绕以川流。深碧不敢俯视。岭人之道京者。其室家有五戒。而兔迁居一焉。其绝险可知。午抵幽谷驿。督邮金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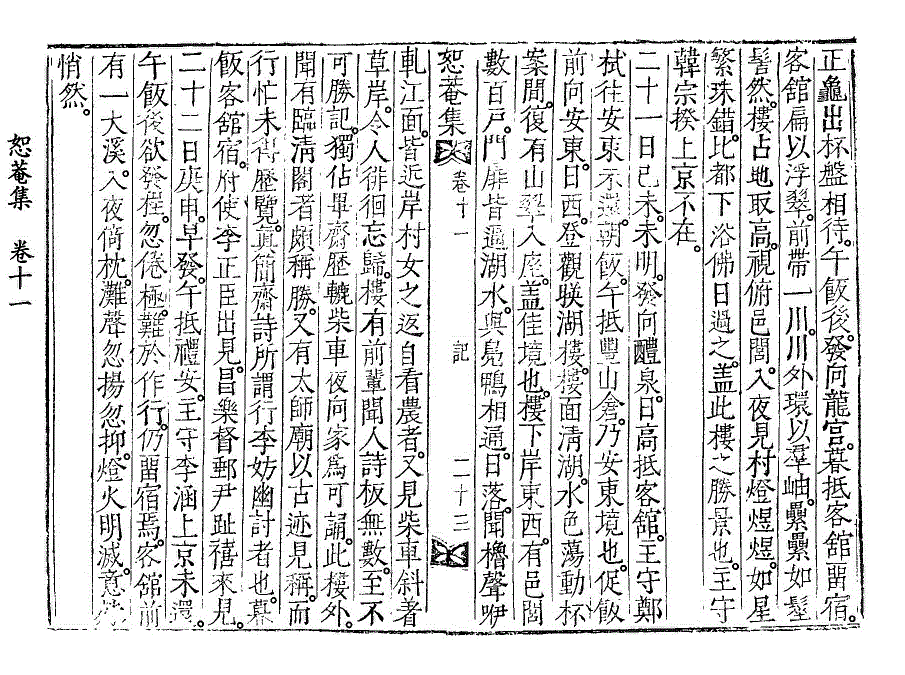 正龟出杯盘相待。午饭后。发向龙宫。暮抵客馆留宿。客馆扁以浮翠。前带一川。川外环以群岫。累累如髽髻然。楼占地取高。视俯邑闾。入夜见村灯煜煜。如星繁珠错。比都下浴佛日过之。盖此楼之胜景也。主守韩宗揆上京不在。
正龟出杯盘相待。午饭后。发向龙宫。暮抵客馆留宿。客馆扁以浮翠。前带一川。川外环以群岫。累累如髽髻然。楼占地取高。视俯邑闾。入夜见村灯煜煜。如星繁珠错。比都下浴佛日过之。盖此楼之胜景也。主守韩宗揆上京不在。二十一日己未。未明。发向醴泉。日高抵客馆。主守郑栻往安东未还。朝饭。午抵丰山仓。乃安东境也。促饭前向安东。日西。登观映湖楼。楼面清湖。水色荡动杯案间。复有山翠入座。盖佳境也。楼下岸东西。有邑闾数百户。门扉皆逼湖水。与凫鸭相通。日落。闻橹声咿轧江面。皆近岸村女之返自看农者。又见柴车斜着草岸。令人徘徊忘归。楼有前辈闻人诗板无数。至不可胜记。独佔毕斋历辘柴车夜向家为可诵。此楼外。闻有临清阁者颇称胜。又有太师庙以古迹见称。而行忙未得历览。真简斋诗所谓行李妨幽讨者也。暮饭客馆宿。府使李正臣出见。昌乐督邮尹趾禧来见。
二十二日庚申。早发。午抵礼安。主守李涵上京未还。午饭后欲发程。忽倦极。难于作行。仍留宿焉。客馆前有一大溪。入夜倚枕。滩声忽扬忽抑。灯火明灭。意殊悄然。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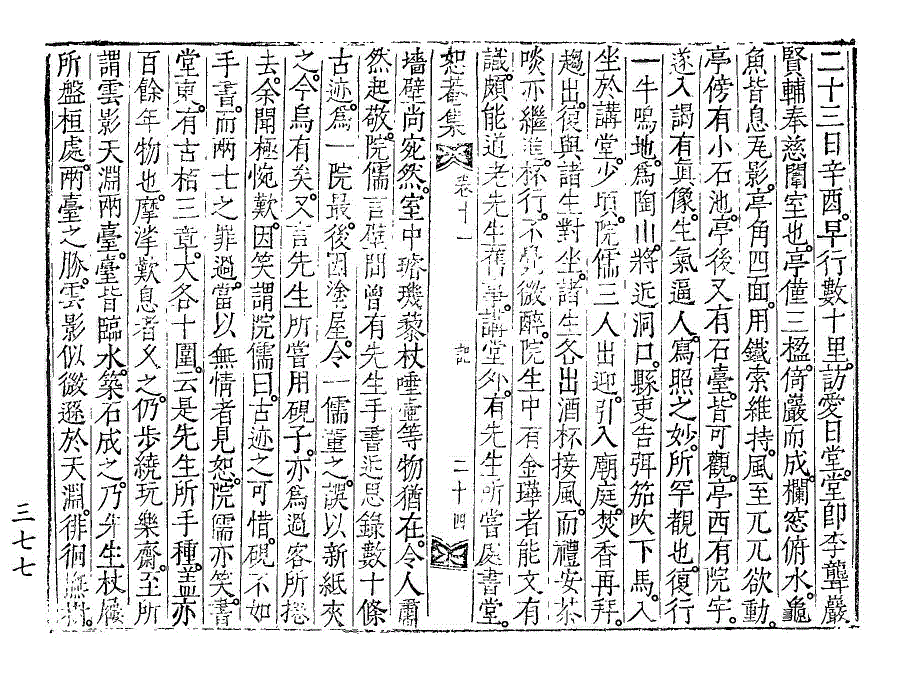 二十三日辛酉。早行数十里。访爱日堂。堂即李聋岩贤辅奉慈闱室也。亭仅三楹。倚岩而成。栏窗俯水。龟鱼皆息瓦影。亭角四面。用铁索维持。风至兀兀欲动。亭傍有小石池。亭后又有石台。皆可观。亭西有院宇。遂入谒有真像。生气逼人。写照之妙。所罕睹也。复行一牛鸣地。为陶山。将近洞口。县吏告弭笳吹下马。入坐于讲堂。少顷。院儒三人出迎。引入庙庭。焚香再拜。趋出。复与诸生对坐。诸生各出酒杯接风。而礼安茶啖亦继进。杯行。不觉微醉。院生中有金璍者能文有识。颇能道老先生旧事。讲堂外。有先生所尝处书堂。墙壁尚宛然。室中璿玑藜杖唾壶等物犹在。令人肃然起敬。院儒言壁间曾有先生手书近思录数十条古迹。为一院最。后因涂屋。令一儒董之。误以新纸夹之。今乌有矣。又言先生所尝用砚子。亦为过客所捲去。余闻极惋叹。因笑谓院儒曰。古迹之可惜。砚不如手书。而两士之罪过。当以无情者见恕。院儒亦笑。书堂东。有古柏三章。大各十围。云是先生所手种。盖亦百馀年物也。摩挲叹息者久之。仍步绕玩乐斋。至所谓云影天渊两台。台皆临水。筑石成之。乃先生杖屦所盘桓处。两台之胜。云影似微逊于天渊。徘徊抚树。
二十三日辛酉。早行数十里。访爱日堂。堂即李聋岩贤辅奉慈闱室也。亭仅三楹。倚岩而成。栏窗俯水。龟鱼皆息瓦影。亭角四面。用铁索维持。风至兀兀欲动。亭傍有小石池。亭后又有石台。皆可观。亭西有院宇。遂入谒有真像。生气逼人。写照之妙。所罕睹也。复行一牛鸣地。为陶山。将近洞口。县吏告弭笳吹下马。入坐于讲堂。少顷。院儒三人出迎。引入庙庭。焚香再拜。趋出。复与诸生对坐。诸生各出酒杯接风。而礼安茶啖亦继进。杯行。不觉微醉。院生中有金璍者能文有识。颇能道老先生旧事。讲堂外。有先生所尝处书堂。墙壁尚宛然。室中璿玑藜杖唾壶等物犹在。令人肃然起敬。院儒言壁间曾有先生手书近思录数十条古迹。为一院最。后因涂屋。令一儒董之。误以新纸夹之。今乌有矣。又言先生所尝用砚子。亦为过客所捲去。余闻极惋叹。因笑谓院儒曰。古迹之可惜。砚不如手书。而两士之罪过。当以无情者见恕。院儒亦笑。书堂东。有古柏三章。大各十围。云是先生所手种。盖亦百馀年物也。摩挲叹息者久之。仍步绕玩乐斋。至所谓云影天渊两台。台皆临水。筑石成之。乃先生杖屦所盘桓处。两台之胜。云影似微逊于天渊。徘徊抚树。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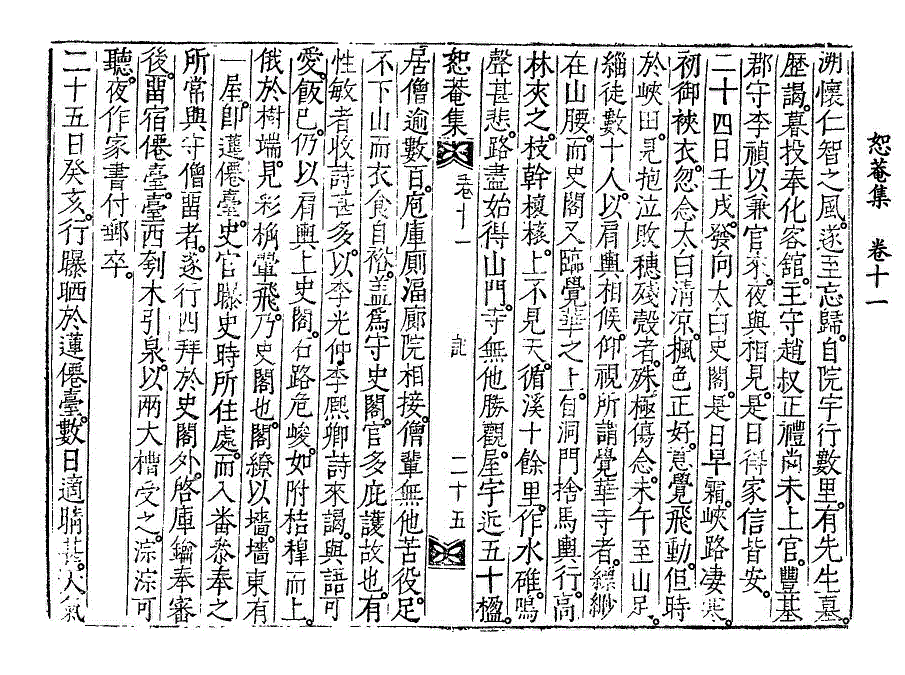 溯怀仁智之风。遂至忘归。自院宇行数里。有先生墓。历谒。暮投奉化客馆。主守赵叔正礼尚未上官。丰基郡守李祯以兼官来。夜与相见。是日得家信皆安。
溯怀仁智之风。遂至忘归。自院宇行数里。有先生墓。历谒。暮投奉化客馆。主守赵叔正礼尚未上官。丰基郡守李祯以兼官来。夜与相见。是日得家信皆安。二十四日壬戌。发向太白史阁。是日早霜。峡路凄寒。初御裌衣。忽念太白清凉。枫色正好。意觉飞动。但时于峡田。见抱泣败穗残壳者。殊极伤念。未午至山足。缁徒数十人。以肩舆相候。仰视所谓觉华寺者。缥缈在山腰。而史阁又临觉华之上。自洞门舍马舆行。高林夹之。枝干𣘨橠。上不见天。循溪十馀里。作水碓。鸣声甚悲。路尽始得山门。寺无他胜观。屋宇近五十楹。居僧逾数百。庖库厕湢廊院相接。僧辈无他苦役。足不下山而衣食自裕。盖为守史阁。官多庇护故也。有性敏者收诗甚多。以李光仲,李熙卿诗来谒。与语可爱。饭已。仍以肩舆上史阁。石路危峻。如附桔槔而上。俄于树端。见彩桷翚飞。乃史阁也。阁缭以墙。墙东有一屋。即莲仙台。史官曝史时所住处。而入番参奉之所常与守僧留者。遂行四拜于史阁外。启库钥奉审后。留宿仙台。台西刳木引泉。以两大槽受之。淙淙可听。夜作家书付邮卒。
二十五日癸亥。行曝晒于莲仙台。数日适晴甚。天气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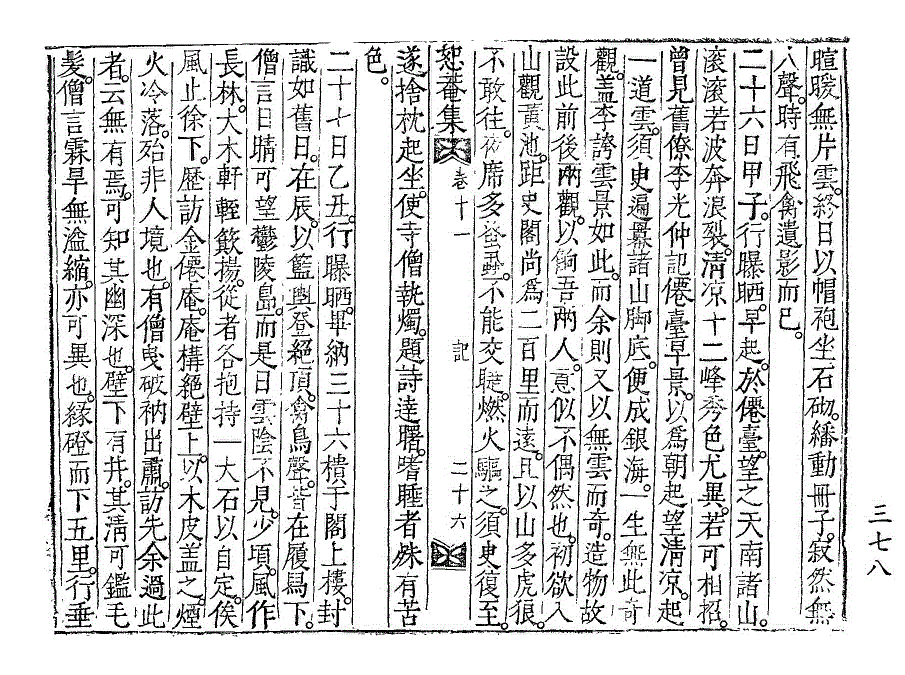 暄暖无片云。终日以帽袍坐石砌。翻动册子。寂然无人声。时有飞禽遗影而已。
暄暖无片云。终日以帽袍坐石砌。翻动册子。寂然无人声。时有飞禽遗影而已。二十六日甲子。行曝晒。早起。于仙台。望之天南诸山。滚滚若波奔浪裂。清凉十二峰秀色尤异。若可相招。曾见旧僚李光仲记仙台早景。以为朝起望清凉。起一道云。须臾遍羃诸山脚底。便成银海。一生无此奇观。盖李誇云景如此。而余则又以无云而奇。造物故设此前后两观。以饷吾两人。意似不偶然也。初欲入山观黄池。距史阁尚为二百里而远。且以山多虎狼。不敢往。夜席多蚤虱。不能交睫。燃火驱之。须臾复至。遂舍枕起坐。使寺僧执烛。题诗达曙。嗜睡者殊有苦色。
二十七日乙丑。行曝晒。毕纳三十六樻于阁上楼。封识如旧日。在辰。以篮舆登绝顶。禽鸟声。皆在履舄下。僧言日晴可望郁陵岛。而是日云阴不见。少顷。风作长林。大木轩轾𥳽扬。从者各抱持一大石以自定。俟风止徐下。历访金仙庵。庵构绝壁上。以木皮盖之。烟火冷落。殆非人境也。有僧曳破衲出肃。访先余过此者。云无有焉。可知其幽深也。壁下有井。其清可鉴毛发。僧言霖旱无溢缩。亦可异也。缘磴而下五里。行垂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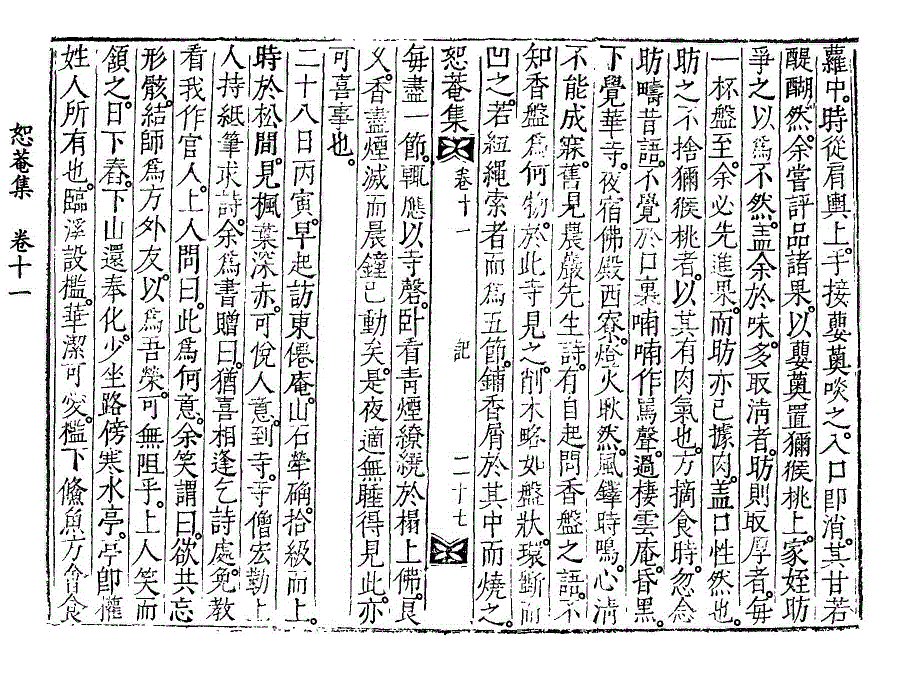 萝中。时从肩舆上。手接蘡薁啖之。入口即消。其甘若醍醐然。余尝评品诸果。以蘡薁置狝猴桃上。家侄昉争之以为不然。盖余于味。多取清者。昉则取厚者。每一杯盘至。余必先进果。而昉亦已据肉。盖口性然也。昉之不舍狝猴桃者。以其有肉气也。方摘食时。忽念昉畴昔语。不觉于口里喃喃作骂声。过栖云庵。昏黑。下觉华寺。夜宿佛殿西寮。灯火耿然。风铎时鸣。心清不能成寐。旧见农岩先生诗。有自起问香盘之语。不知香盘为何物。于此寺见之。削木略如盘状。环斲而凹之。若纽绳索者而为五节。铺香屑于其中而烧之。每尽一节。辄应以寺磬。卧看青烟缭绕于榻上佛。良久。香尽烟灭而晨钟已动矣。是夜适无睡得见此。亦可喜事也。
萝中。时从肩舆上。手接蘡薁啖之。入口即消。其甘若醍醐然。余尝评品诸果。以蘡薁置狝猴桃上。家侄昉争之以为不然。盖余于味。多取清者。昉则取厚者。每一杯盘至。余必先进果。而昉亦已据肉。盖口性然也。昉之不舍狝猴桃者。以其有肉气也。方摘食时。忽念昉畴昔语。不觉于口里喃喃作骂声。过栖云庵。昏黑。下觉华寺。夜宿佛殿西寮。灯火耿然。风铎时鸣。心清不能成寐。旧见农岩先生诗。有自起问香盘之语。不知香盘为何物。于此寺见之。削木略如盘状。环斲而凹之。若纽绳索者而为五节。铺香屑于其中而烧之。每尽一节。辄应以寺磬。卧看青烟缭绕于榻上佛。良久。香尽烟灭而晨钟已动矣。是夜适无睡得见此。亦可喜事也。二十八日丙寅。早起访东仙庵。山石荦确。拾级而上。时于松间。见枫叶深赤。可悦人意。到寺。寺僧宏勒上人持纸笔求诗。余为书赠曰。犹喜相逢乞诗处。免教看我作官人。上人问曰。此为何意。余笑谓曰。欲共忘形骸。结师为方外友。以为吾荣。可无阻乎。上人笑而颔之。日下舂。下山还奉化。少坐路傍寒水亭。亭即权姓人所有也。临溪设槛。华洁可爱。槛下鯈鱼方会食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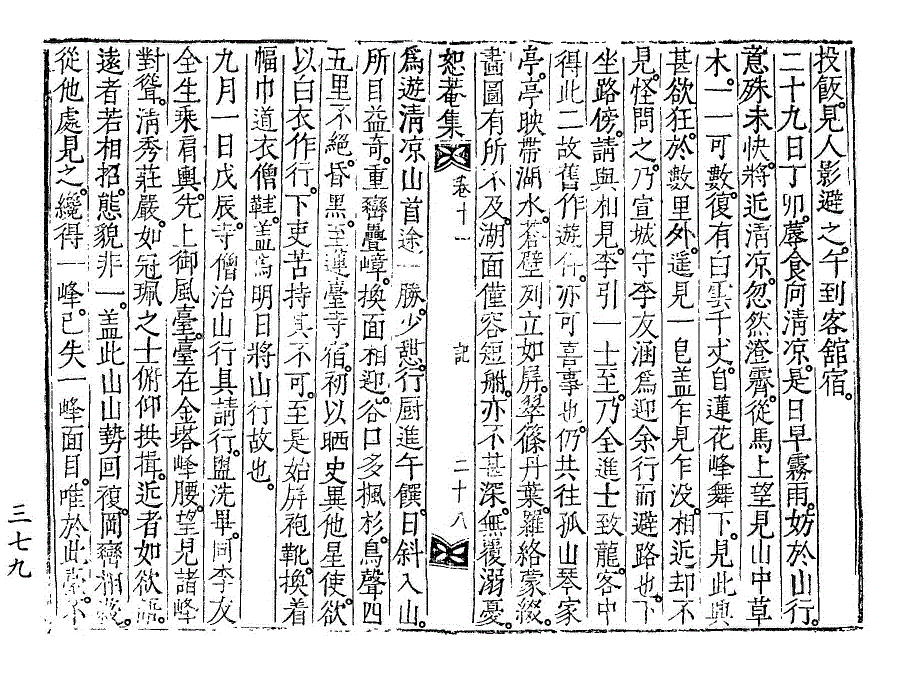 投饭。见人影避之。午到客馆宿。
投饭。见人影避之。午到客馆宿。二十九日丁卯。蓐食向清凉。是日早雾雨。妨于山行。意殊未快。将近清凉。忽然澄霁。从马上望见山中草木。一一可数。复有白云千丈。自莲花峰舞下。见此兴甚欲狂。于数里外。遥见一皂盖乍见乍没。相近却不见。怪问之。乃宣城守李友涵为迎余行而避路也。下坐路傍。请与相见。李引一士至。乃全进士致龙。客中得此二故旧作游伴。亦可喜事也。仍共往孤山琴家亭。亭映带湖水。苍壁列立如屏。翠筱丹叶。罗络蒙缀。画图有所不及。湖面仅容短䑧。亦不甚深。无覆溺忧。为游清凉山首途一胜。少憩。行厨进午馔。日斜入山。所目益奇。重峦叠嶂。换面相迎。谷口多枫杉。鸟声四五里不绝。昏黑。至莲台寺宿。初以晒史异他星使。欲以白衣作行。下吏苦持其不可。至是始屏袍靴。换着幅巾道衣僧鞋。盖为明日将山行故也。
九月一日戊辰。寺僧治山行具请行。盥洗毕。同李友全生乘肩舆。先上御风台。台在金塔峰腰。望见诸峰对耸。清秀庄严。如冠佩之士俯仰拱揖。近者如欲语。远者若相招。态貌非一。盖此山山势回复。冈峦相蔽。从他处见之。才得一峰。已失一峰面目。唯于此台。不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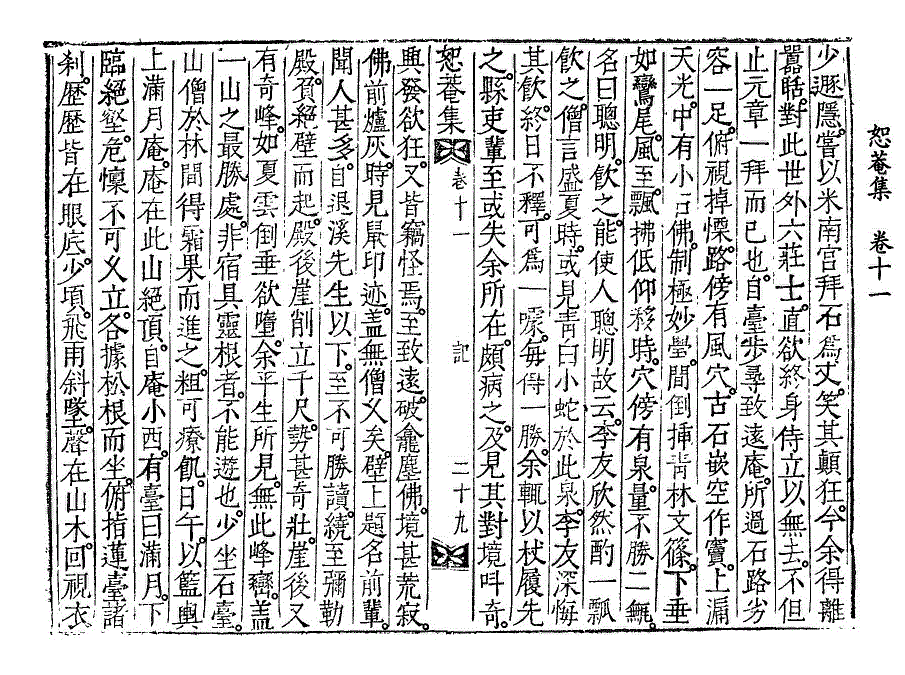 少遁隐。尝以米南宫拜石为丈。笑其颠狂。今余得离嚣聒。对此世外六庄士。直欲终身侍立以无去。不但止元章一拜而已也。自台步寻致远庵。所过石路劣容一足。俯视掉慄。路傍有风穴。古石嵌空作窦。上漏天光。中有小石佛。制极妙璺。间倒插青林文筱。下垂如鸾尾。风至。飘拂低仰移时。穴傍有泉。量不胜二甒。名曰聪明。饮之。能使人聪明故云。李友欣然酌一瓢饮之。僧言盛夏时。或见青白小蛇于此泉。李友深悔其饮。终日不释。可为一噱。每得一胜。余辄以杖履先之。县吏辈至或失余所在。颇病之。及见其对境叫奇。兴发欲狂。又皆窃怪焉。至致远。破龛尘佛。境甚荒寂。佛前炉灰。时见鼠印迹。盖无僧久矣。壁上题名前辈。闻人甚多。自退溪先生以下。至不可胜读。绕至弥勒殿。负绝壁而起。殿后崖削立千尺。势甚奇壮。崖后又有奇峰。如夏云倒垂欲堕。余平生所见。无此峰峦。盖一山之最胜处。非宿具灵根者。不能游也。少坐石台。山僧于林间得霜果而进之。粗可疗饥。日午。以篮舆上满月庵。庵在此山绝顶。自庵小西。有台曰满月。下临绝壑。危懔不可久立。各据松根而坐。俯指莲台诸刹。历历皆在眼底。少顷。飞雨斜坠。声在山木。回视衣
少遁隐。尝以米南宫拜石为丈。笑其颠狂。今余得离嚣聒。对此世外六庄士。直欲终身侍立以无去。不但止元章一拜而已也。自台步寻致远庵。所过石路劣容一足。俯视掉慄。路傍有风穴。古石嵌空作窦。上漏天光。中有小石佛。制极妙璺。间倒插青林文筱。下垂如鸾尾。风至。飘拂低仰移时。穴傍有泉。量不胜二甒。名曰聪明。饮之。能使人聪明故云。李友欣然酌一瓢饮之。僧言盛夏时。或见青白小蛇于此泉。李友深悔其饮。终日不释。可为一噱。每得一胜。余辄以杖履先之。县吏辈至或失余所在。颇病之。及见其对境叫奇。兴发欲狂。又皆窃怪焉。至致远。破龛尘佛。境甚荒寂。佛前炉灰。时见鼠印迹。盖无僧久矣。壁上题名前辈。闻人甚多。自退溪先生以下。至不可胜读。绕至弥勒殿。负绝壁而起。殿后崖削立千尺。势甚奇壮。崖后又有奇峰。如夏云倒垂欲堕。余平生所见。无此峰峦。盖一山之最胜处。非宿具灵根者。不能游也。少坐石台。山僧于林间得霜果而进之。粗可疗饥。日午。以篮舆上满月庵。庵在此山绝顶。自庵小西。有台曰满月。下临绝壑。危懔不可久立。各据松根而坐。俯指莲台诸刹。历历皆在眼底。少顷。飞雨斜坠。声在山木。回视衣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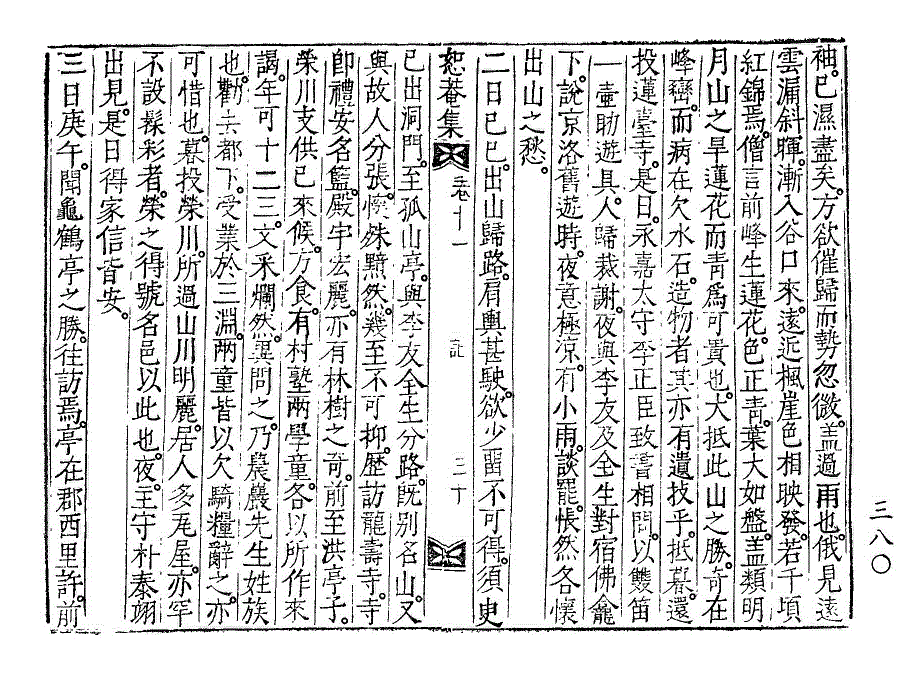 袖。已湿尽矣。方欲催归而势忽微。盖过雨也。俄见远云漏斜晖。渐入谷口来。远近枫崖色相映发。若千顷红锦焉。僧言前峰生莲花。色正青。叶大如盘。盖类明月山之旱莲花而青为可贵也。大抵此山之胜。奇在峰峦。而病在欠水石。造物者其亦有遗技乎。抵暮。还投莲台寺。是日。永嘉太守李正臣致书相问。以双笛一壶助游具。人归裁谢。夜与李友及全生对宿佛龛下。说京洛旧游时。夜意极凉。有小雨。谈罢。怅然各怀出山之愁。
袖。已湿尽矣。方欲催归而势忽微。盖过雨也。俄见远云漏斜晖。渐入谷口来。远近枫崖色相映发。若千顷红锦焉。僧言前峰生莲花。色正青。叶大如盘。盖类明月山之旱莲花而青为可贵也。大抵此山之胜。奇在峰峦。而病在欠水石。造物者其亦有遗技乎。抵暮。还投莲台寺。是日。永嘉太守李正臣致书相问。以双笛一壶助游具。人归裁谢。夜与李友及全生对宿佛龛下。说京洛旧游时。夜意极凉。有小雨。谈罢。怅然各怀出山之愁。二日己巳。出山归路。肩舆甚驶。欲少留不可得。须臾已出洞门。至孤山亭。与李友全生分路。既别名山。又与故人分张。怀殊黯然。几至不可抑。历访龙寿寺。寺即礼安名篮。殿宇宏丽。亦有林树之奇。前至洪亭子。荣川支供已来候。方食。有村塾两学童。各以所作来谒。年可十二三。文采烂然。异问之。乃农岩先生姓族也。劝去都下。受业于三渊。两童皆以欠骑粮辞之。亦可惜也。暮投荣川。所过山川明丽。居人多瓦屋。亦罕不设髹彩者。荣之得号名邑以此也。夜。主守朴泰翊出见。是日得家信皆安。
三日庚午。闻龟鹤亭之胜。往访焉。亭在郡西里许。前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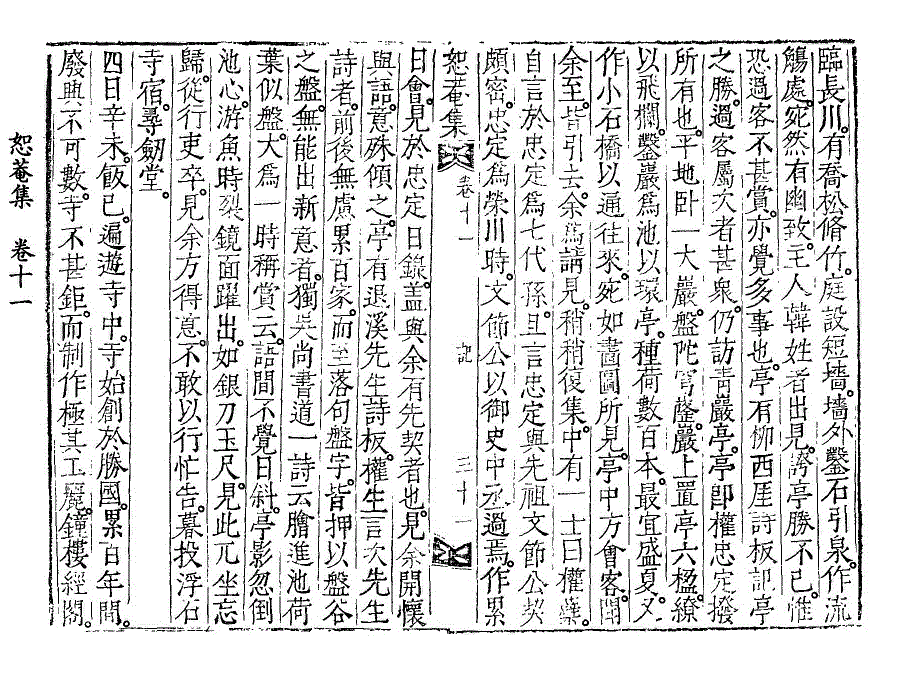 临长川。有乔松脩竹。庭设短墙。墙外凿石引泉。作流觞处。宛然有幽致。主人韩姓者出见。誇亭胜不已。惟恐过客不甚赏。亦觉多事也。亭有柳西厓诗板记亭之胜。过客属次者甚众。仍访青岩亭。亭即权忠定拨所有也。平地卧一大岩。盘陀穹隆。岩上置亭六楹。缭以飞栏。凿岩为池以环亭。种荷数百本。最宜盛夏。又作小石桥以通往来。宛如画图所见。亭中方会客。闻余至。皆引去。余为请见。稍稍复集。中有一士曰权檗。自言于忠定为七代孙。且言忠定与先祖文节公契颇密。忠定为荣川时。文节公以御史中丞过焉。作累日会。见于忠定日录。盖与余有先契者也。见余开怀与语。意殊倾之。亭有退溪先生诗板。权生言次先生诗者。前后无虑累百家。而至落句盘字。皆押以盘谷之盘。无能出新意者。独吴尚书道一诗云脍进池荷叶似盘。大为一时称赏云。语间不觉日斜。亭影忽倒池心。游鱼时裂镜面跃出。如银刀玉尺。见此兀坐忘归。从行吏卒。见余方得意。不敢以行忙告。暮投浮石寺宿。寻剑堂。
临长川。有乔松脩竹。庭设短墙。墙外凿石引泉。作流觞处。宛然有幽致。主人韩姓者出见。誇亭胜不已。惟恐过客不甚赏。亦觉多事也。亭有柳西厓诗板记亭之胜。过客属次者甚众。仍访青岩亭。亭即权忠定拨所有也。平地卧一大岩。盘陀穹隆。岩上置亭六楹。缭以飞栏。凿岩为池以环亭。种荷数百本。最宜盛夏。又作小石桥以通往来。宛如画图所见。亭中方会客。闻余至。皆引去。余为请见。稍稍复集。中有一士曰权檗。自言于忠定为七代孙。且言忠定与先祖文节公契颇密。忠定为荣川时。文节公以御史中丞过焉。作累日会。见于忠定日录。盖与余有先契者也。见余开怀与语。意殊倾之。亭有退溪先生诗板。权生言次先生诗者。前后无虑累百家。而至落句盘字。皆押以盘谷之盘。无能出新意者。独吴尚书道一诗云脍进池荷叶似盘。大为一时称赏云。语间不觉日斜。亭影忽倒池心。游鱼时裂镜面跃出。如银刀玉尺。见此兀坐忘归。从行吏卒。见余方得意。不敢以行忙告。暮投浮石寺宿。寻剑堂。四日辛未。饭已。遍游寺中。寺始创于胜国。累百年间。废兴不可数。寺不甚钜。而制作极其工丽。钟楼经阁。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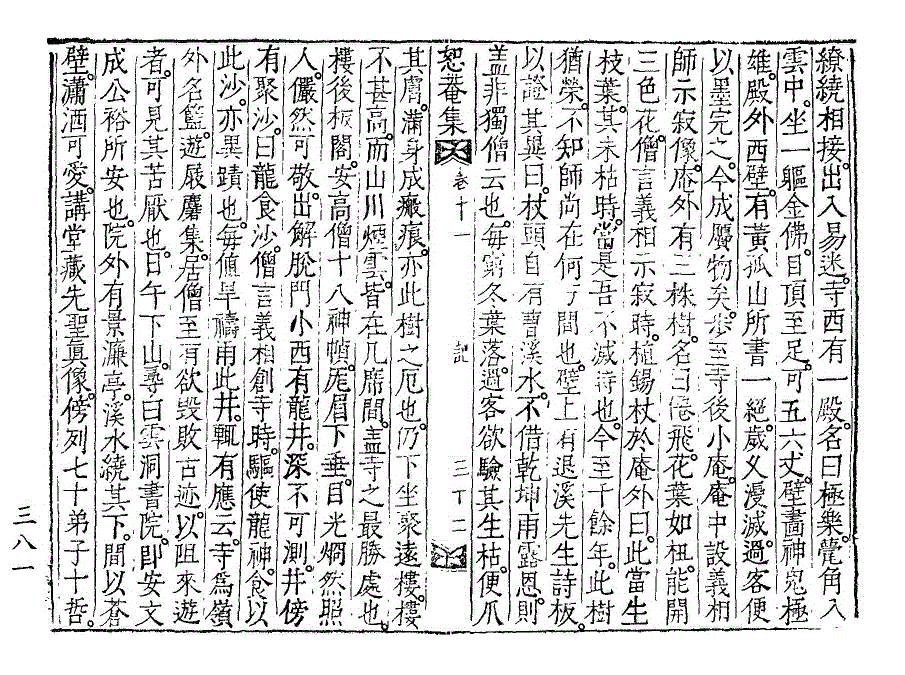 缭绕相接。出入易迷。寺西有一殿。名曰极乐。甍角入云中。坐一躯金佛。自顶至足。可五六丈。壁画神鬼极雄。殿外西壁。有黄孤山所书一绝。岁久漫灭。过客便以墨完之。今成赝物矣。步至寺后小庵。庵中设义相师示寂像。庵外有三株树。名曰仙飞。花叶如杻。能开三色花。僧言义相示寂时。植锡杖于庵外曰。此当生枝叶。其未枯时。当是吾不灭时也。今至千馀年。此树犹荣。不知师尚在何方间也。壁上有退溪先生诗板。以證其异曰。杖头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则盖非独僧云也。每穷冬叶落。过客欲验其生枯。便爪其肤。满身成瘢痕。亦此树之厄也。仍下坐聚远楼。楼不甚高。而山川烟云。皆在几席间。盖寺之最胜处也。楼后板阁。安高僧十八神帧。厖眉下垂。目光烱然照人。俨然可敬。出解脱门小西有龙井。深不可测。井傍有聚沙。曰龙食沙。僧言义相创寺时。驱使龙神。食以此沙。亦异迹也。每值旱祷雨此井。辄有应云。寺为岭外名篮。游屐麇集。居僧至有欲毁败古迹。以阻来游者。可见其苦厌也。日午下山。寻白云洞书院。即安文成公裕所安也。院外有景濂亭。溪水绕其下。间以苍壁。潇洒可爱。讲堂藏先圣真像。傍列七十弟子十哲。
缭绕相接。出入易迷。寺西有一殿。名曰极乐。甍角入云中。坐一躯金佛。自顶至足。可五六丈。壁画神鬼极雄。殿外西壁。有黄孤山所书一绝。岁久漫灭。过客便以墨完之。今成赝物矣。步至寺后小庵。庵中设义相师示寂像。庵外有三株树。名曰仙飞。花叶如杻。能开三色花。僧言义相示寂时。植锡杖于庵外曰。此当生枝叶。其未枯时。当是吾不灭时也。今至千馀年。此树犹荣。不知师尚在何方间也。壁上有退溪先生诗板。以證其异曰。杖头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则盖非独僧云也。每穷冬叶落。过客欲验其生枯。便爪其肤。满身成瘢痕。亦此树之厄也。仍下坐聚远楼。楼不甚高。而山川烟云。皆在几席间。盖寺之最胜处也。楼后板阁。安高僧十八神帧。厖眉下垂。目光烱然照人。俨然可敬。出解脱门小西有龙井。深不可测。井傍有聚沙。曰龙食沙。僧言义相创寺时。驱使龙神。食以此沙。亦异迹也。每值旱祷雨此井。辄有应云。寺为岭外名篮。游屐麇集。居僧至有欲毁败古迹。以阻来游者。可见其苦厌也。日午下山。寻白云洞书院。即安文成公裕所安也。院外有景濂亭。溪水绕其下。间以苍壁。潇洒可爱。讲堂藏先圣真像。傍列七十弟子十哲。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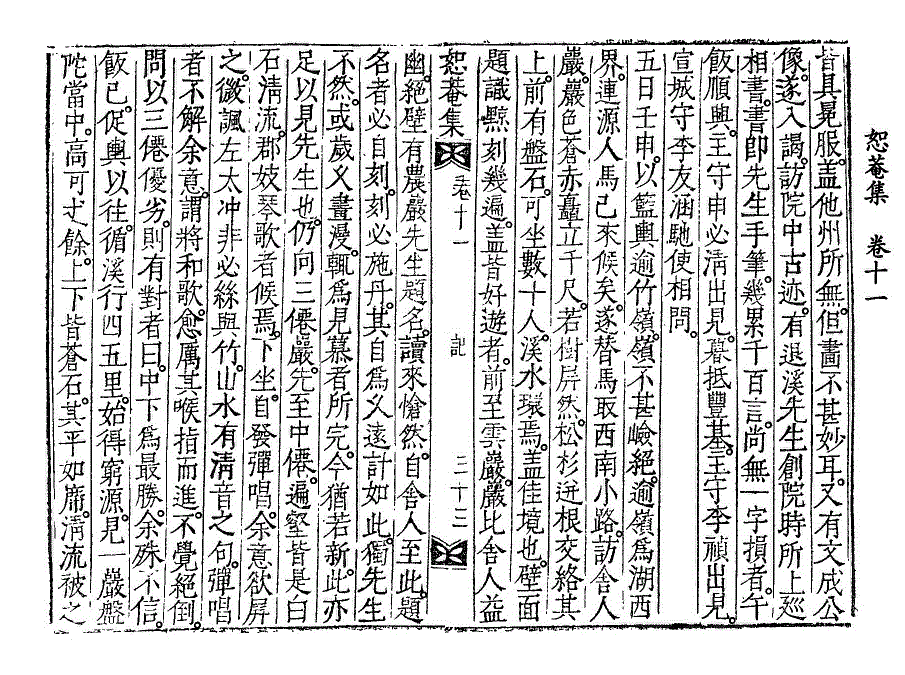 皆具冕服。盖他州所无。但画不甚妙耳。又有文成公像。遂入谒。访院中古迹。有退溪先生创院时所上巡相书。书即先生手笔。几累千百言。尚无一字损者。午饭顺兴。主守申必清出见。暮抵丰基。主守李祯出见。宣城守李友涵驰使相问。
皆具冕服。盖他州所无。但画不甚妙耳。又有文成公像。遂入谒。访院中古迹。有退溪先生创院时所上巡相书。书即先生手笔。几累千百言。尚无一字损者。午饭顺兴。主守申必清出见。暮抵丰基。主守李祯出见。宣城守李友涵驰使相问。五日壬申。以篮舆逾竹岭。岭不甚崄绝。逾岭为湖西界。连源人马已来候矣。遂替马取西南小路。访舍人岩。岩色苍赤矗立千尺。若树屏然。松杉迸根交络其上。前有盘石。可坐数十人。溪水环焉。盖佳境也。壁面题识黥刻几遍。盖皆好游者。前至云岩。岩比舍人益幽。绝壁有农岩先生题名。读来怆然。自舍人至此。题名者必自刻。刻必施丹。其自为久远计如此。独先生不然。或岁久画漫。辄为见慕者所完。今犹若新。此亦足以见先生也。仍向三仙岩。先至中仙。遍壑皆是白石清流。郡妓琴歌者候焉。下坐。自发弹唱。余意欲屏之。微讽左太冲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之句。弹唱者不解余意。谓将和歌。愈厉其喉指而进。不觉绝倒。问以三仙优劣。则有对者曰。中下为最胜。余殊不信。饭已。促舆以往。循溪行四五里。始得穷源。见一岩盘陀当中。高可丈馀。上下皆苍石。其平如席。清流被之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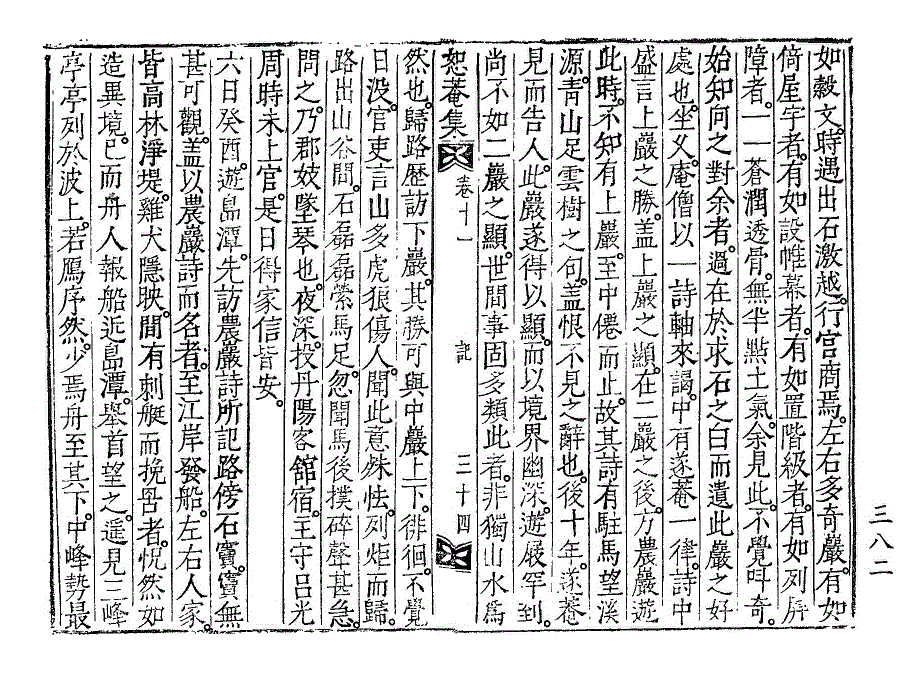 如縠文。时遇出石激越。行宫商焉。左右多奇岩。有如倚屋宇者。有如设帷幕者。有如置阶级者。有如列屏障者。一一苍润透骨。无半点土气。余见此。不觉叫奇。始知向之对余者。过在于求石之白而遗此岩之好处也。坐久。庵僧以一诗轴来谒。中有遂庵一律。诗中盛言上岩之胜。盖上岩之显。在二岩之后。方农岩游此时。不知有上岩。至中仙而止。故其诗有驻马望溪源。青山足云树之句。盖恨不见之辞也。后十年。遂庵见而告人。此岩遂得以显。而以境界幽深。游屐罕到。尚不如二岩之显。世间事固多类此者。非独山水为然也。归路历访下岩。其胜可与中岩上下。徘徊。不觉日没。官吏言山多虎狼伤人。闻此意殊怯。列炬而归。路出山谷间。石磊磊萦马足。忽闻马后扑碎声甚急。问之。乃郡妓坠琴也。夜深。投丹阳客馆宿。主守吕光周时未上官。是日得家信皆安。
如縠文。时遇出石激越。行宫商焉。左右多奇岩。有如倚屋宇者。有如设帷幕者。有如置阶级者。有如列屏障者。一一苍润透骨。无半点土气。余见此。不觉叫奇。始知向之对余者。过在于求石之白而遗此岩之好处也。坐久。庵僧以一诗轴来谒。中有遂庵一律。诗中盛言上岩之胜。盖上岩之显。在二岩之后。方农岩游此时。不知有上岩。至中仙而止。故其诗有驻马望溪源。青山足云树之句。盖恨不见之辞也。后十年。遂庵见而告人。此岩遂得以显。而以境界幽深。游屐罕到。尚不如二岩之显。世间事固多类此者。非独山水为然也。归路历访下岩。其胜可与中岩上下。徘徊。不觉日没。官吏言山多虎狼伤人。闻此意殊怯。列炬而归。路出山谷间。石磊磊萦马足。忽闻马后扑碎声甚急。问之。乃郡妓坠琴也。夜深。投丹阳客馆宿。主守吕光周时未上官。是日得家信皆安。六日癸酉。游岛潭。先访农岩诗所记路傍石窦。窦无甚可观。盖以农岩诗而名者。至江岸发船。左右人家。皆高林净堤。鸡犬隐映。间有刺艇而挽罟者。恍然如造异境。已而舟人报船近岛潭。举首望之。遥见三峰亭亭列于波上。若雁序然。少焉舟至其下。中峰势最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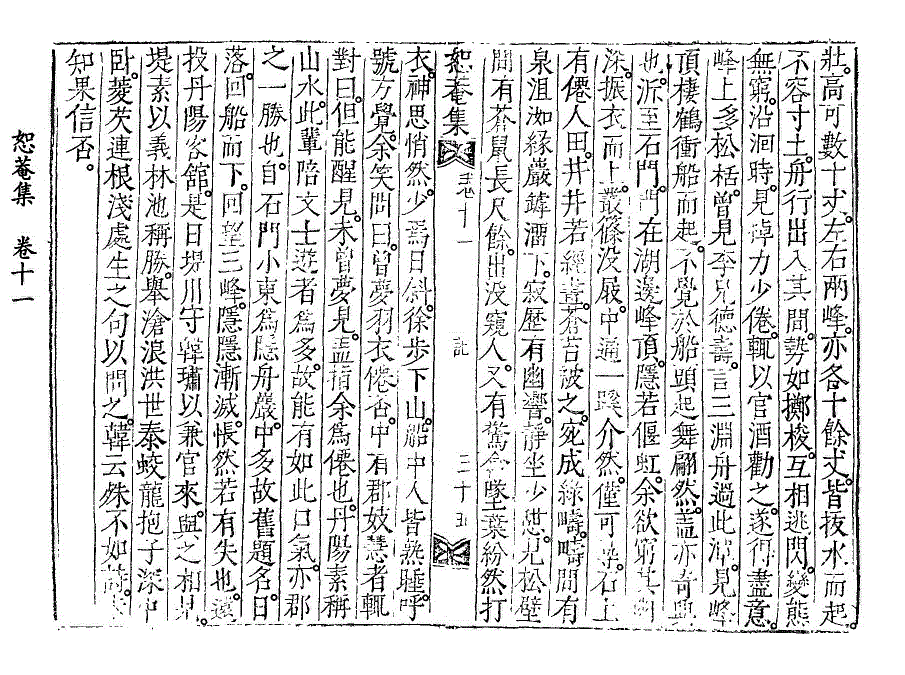 壮。高可数十丈。左右两峰。亦各十馀丈。皆拔水而起。不容寸土。舟行出入其间。势如掷梭。互相逃闪。变态无穷。沿洄时。见棹力少倦。辄以官酒劝之。遂得尽意。峰上多松栝。曾见李兄德寿。言三渊舟过此潭。见峰顶栖鹤冲船而起。不觉于船头起舞翩然。盖亦奇兴也。溯至石门。门在湖边峰顶。隐若偃虹。余欲穷其幽深。振衣而上。丛筱没屐。中通一蹊介然。仅可寻。石上有仙人田。井井若经画。苍苔被之。宛成绿畴。畴间有泉沮洳缘岩罅溜下。寂历有幽响。静坐少憩。见松壁间有苍鼠长尺馀。出没窥人。又有惊禽坠叶纷然打衣。神思悄然。少焉日斜。徐步下山。船中人皆熟睡。呼号方觉。余笑问曰。曾梦羽衣仙否。中有郡妓慧者辄对曰。但能醒见。未曾梦见。盖指余为仙也。丹阳素称山水。此辈陪文士游者为多。故能有如此口气。亦郡之一胜也。自石门小东为隐舟岩。中多故旧题名。日落。回船而下。回望三峰。隐隐渐灭。怅然若有失也。还投丹阳客馆。是日堤川守韩璛以兼官来。与之相见。堤素以义林池称胜。举沧浪洪世泰蛟龙抱子深中卧。菱芡连根浅处生之句以问之。韩云殊不如诗。未知果信否。
壮。高可数十丈。左右两峰。亦各十馀丈。皆拔水而起。不容寸土。舟行出入其间。势如掷梭。互相逃闪。变态无穷。沿洄时。见棹力少倦。辄以官酒劝之。遂得尽意。峰上多松栝。曾见李兄德寿。言三渊舟过此潭。见峰顶栖鹤冲船而起。不觉于船头起舞翩然。盖亦奇兴也。溯至石门。门在湖边峰顶。隐若偃虹。余欲穷其幽深。振衣而上。丛筱没屐。中通一蹊介然。仅可寻。石上有仙人田。井井若经画。苍苔被之。宛成绿畴。畴间有泉沮洳缘岩罅溜下。寂历有幽响。静坐少憩。见松壁间有苍鼠长尺馀。出没窥人。又有惊禽坠叶纷然打衣。神思悄然。少焉日斜。徐步下山。船中人皆熟睡。呼号方觉。余笑问曰。曾梦羽衣仙否。中有郡妓慧者辄对曰。但能醒见。未曾梦见。盖指余为仙也。丹阳素称山水。此辈陪文士游者为多。故能有如此口气。亦郡之一胜也。自石门小东为隐舟岩。中多故旧题名。日落。回船而下。回望三峰。隐隐渐灭。怅然若有失也。还投丹阳客馆。是日堤川守韩璛以兼官来。与之相见。堤素以义林池称胜。举沧浪洪世泰蛟龙抱子深中卧。菱芡连根浅处生之句以问之。韩云殊不如诗。未知果信否。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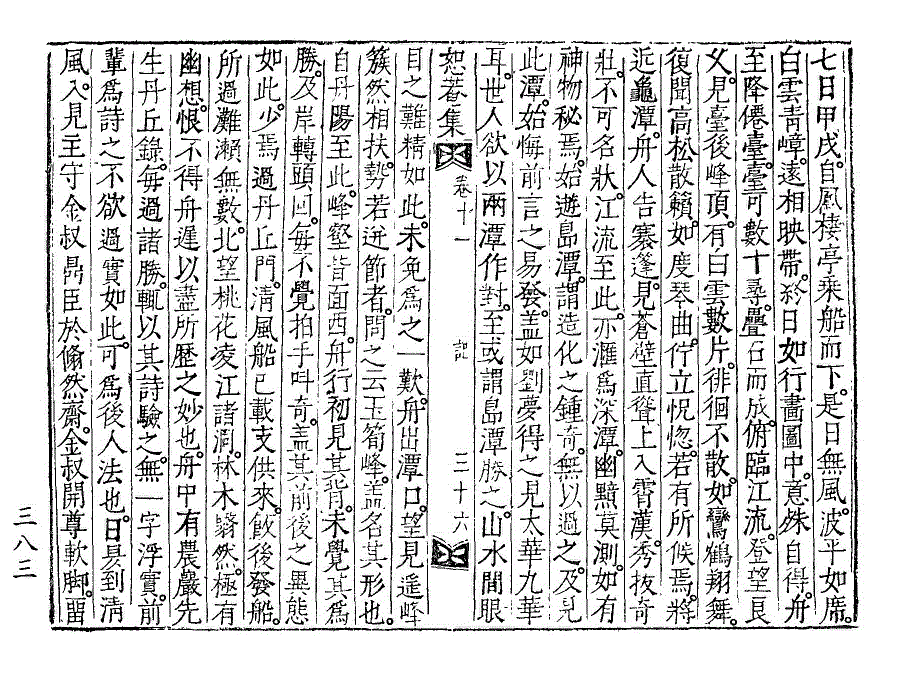 七日甲戌。自凤栖亭乘船而下。是日无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远相映带。终日如行画图中。意殊自得。舟至降仙台。台可数十寻。叠石而成。俯临江流。登望良久。见台后峰顶。有白云数片。徘徊不散。如鸾鹤翔舞。复闻高松散籁。如度琴曲。伫立恍惚。若有所候焉。将近龟潭。舟人告褰篷。见苍壁直耸上入霄汉。秀拔奇壮。不可名状。江流至此。亦𣿬为深潭。幽黯莫测。如有神物秘焉。始游岛潭。谓造化之钟奇。无以过之。及见此潭。始悔前言之易发。盖如刘梦得之见太华九华耳。世人欲以两潭作对。至或谓岛潭胜之。山水间眼目之难精如此。未免为之一叹。舟出潭口。望见遥峰簇然相扶。势若迸节者。问之云玉笋峰。盖名其形也。自丹阳至此。峰壑皆面西。舟行初见其背。未觉其为胜。及岸转头回。每不觉拍手叫奇。盖其前后之异态如此。少焉过丹丘门。清风船已载支供来。饭后发船。所过滩濑无数。北望桃花凌江诸洞。林木翳然。极有幽想。恨不得舟迟以尽所历之妙也。舟中有农岩先生丹丘录。每过诸胜。辄以其诗验之。无一字浮实。前辈为诗之不欲过实如此。可为后人法也。日昃到清风。入见主守金叔鼎臣于翛然斋。金叔开尊软脚。留
七日甲戌。自凤栖亭乘船而下。是日无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远相映带。终日如行画图中。意殊自得。舟至降仙台。台可数十寻。叠石而成。俯临江流。登望良久。见台后峰顶。有白云数片。徘徊不散。如鸾鹤翔舞。复闻高松散籁。如度琴曲。伫立恍惚。若有所候焉。将近龟潭。舟人告褰篷。见苍壁直耸上入霄汉。秀拔奇壮。不可名状。江流至此。亦𣿬为深潭。幽黯莫测。如有神物秘焉。始游岛潭。谓造化之钟奇。无以过之。及见此潭。始悔前言之易发。盖如刘梦得之见太华九华耳。世人欲以两潭作对。至或谓岛潭胜之。山水间眼目之难精如此。未免为之一叹。舟出潭口。望见遥峰簇然相扶。势若迸节者。问之云玉笋峰。盖名其形也。自丹阳至此。峰壑皆面西。舟行初见其背。未觉其为胜。及岸转头回。每不觉拍手叫奇。盖其前后之异态如此。少焉过丹丘门。清风船已载支供来。饭后发船。所过滩濑无数。北望桃花凌江诸洞。林木翳然。极有幽想。恨不得舟迟以尽所历之妙也。舟中有农岩先生丹丘录。每过诸胜。辄以其诗验之。无一字浮实。前辈为诗之不欲过实如此。可为后人法也。日昃到清风。入见主守金叔鼎臣于翛然斋。金叔开尊软脚。留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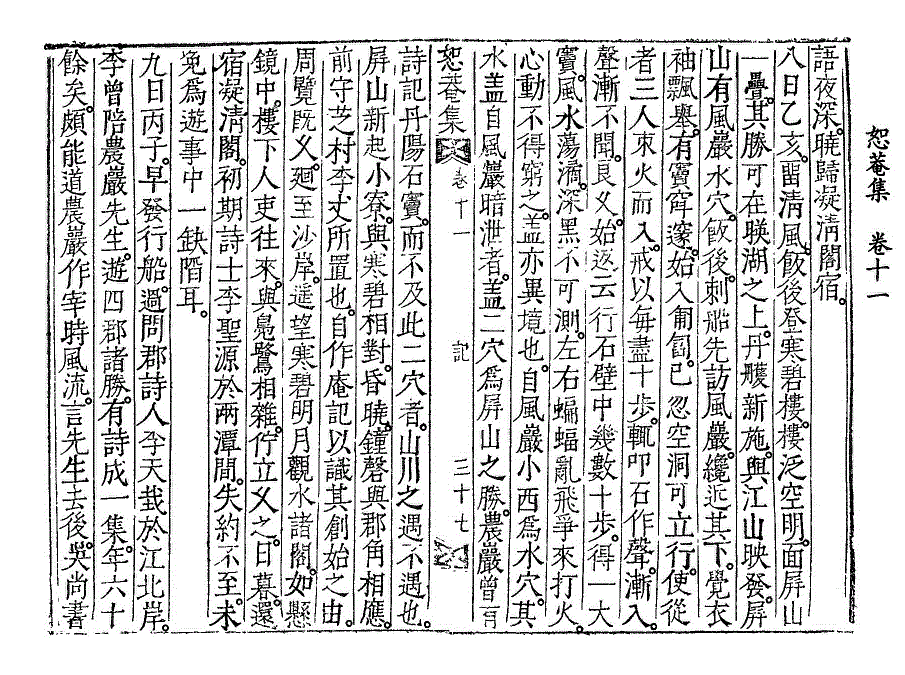 语夜深。晓归凝清阁宿。
语夜深。晓归凝清阁宿。八日乙亥。留清风。饭后登寒碧楼。楼泛空明。面屏山一叠。其胜可在映湖之上。丹雘新施。与江山映发。屏山有风岩水穴。饭后。刺船先访风岩。才近其下。觉衣袖飘举。有窦䆗邃。始入匍匐。已忽空洞可立行。使从者三人束火而入。戒以每尽十步。辄叩石作声。渐入。声渐不闻。良久。始返云行石壁中几数十步。得一大窦。风水荡潏。深黑不可测。左右蝙蝠乱飞争来打火。心动不得穷之。盖亦异境也。自风岩小西为水穴。其水盖自风岩暗泄者。盖二穴为屏山之胜。农岩曾有诗记丹阳石窦。而不及此二穴者。山川之遇不遇也。屏山新起小寮。与寒碧相对。昏晓。钟磬与郡角相应。前守芝村李丈所置也。自作庵记以识其创始之由。周览既久。回至沙岸。遥望寒碧明月观水诸阁。如悬镜中。楼下人吏往来。与凫鹭相杂。伫立久之。日暮。还宿凝清阁。初期诗士李圣源于两潭间。失约不至。未免为游事中一缺陷耳。
九日丙子。早发行船。过问郡诗人李天㘽于江北岸。李曾陪农岩先生。游四郡诸胜。有诗成一集。年六十馀矣。颇能道农岩作宰时风流。言先生去后。吴尚书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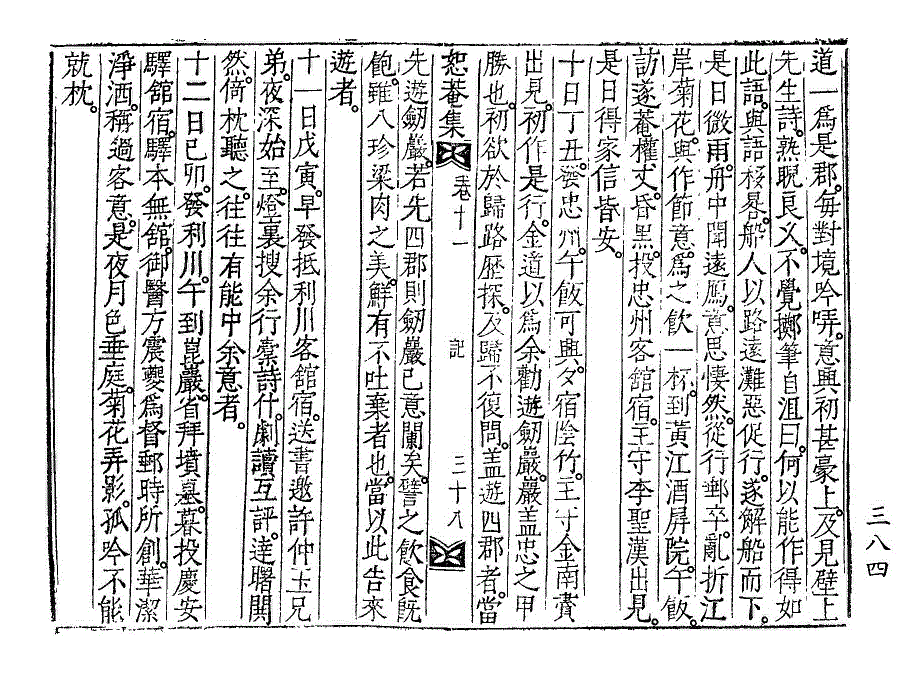 道一为是郡。每对境吟哢。意兴初甚豪上。及见壁上先生诗。熟睨良久。不觉掷笔自沮曰。何以能作得如此语。与语移晷。船人以路远滩恶促行。遂解船而下。是日微雨。舟中闻远雁。意思悽然。从行邮卒。乱折江岸菊花。与作节意。为之饮一杯。到黄江酒屏院。午饭。访遂庵权丈。昏黑。投忠州客馆宿。主守李圣汉出见。是日得家信皆安。
道一为是郡。每对境吟哢。意兴初甚豪上。及见壁上先生诗。熟睨良久。不觉掷笔自沮曰。何以能作得如此语。与语移晷。船人以路远滩恶促行。遂解船而下。是日微雨。舟中闻远雁。意思悽然。从行邮卒。乱折江岸菊花。与作节意。为之饮一杯。到黄江酒屏院。午饭。访遂庵权丈。昏黑。投忠州客馆宿。主守李圣汉出见。是日得家信皆安。十日丁丑。发忠州。午饭可兴。夕宿阴竹。主守金南赆出见。初作是行。金道以为余劝游剑岩。岩盖忠之甲胜也。初欲于归路历探。及归不复问。盖游四郡者。当先游剑岩。若先四郡则剑岩已意阑矣。譬之饮食既饱。虽八珍粱肉之美。鲜有不吐弃者也。当以此告来游者。
十一日戊寅。早发抵利川客馆宿。送书邀许仲玉兄弟。夜深始至。灯里搜余行橐诗什。剧读互评。达曙閧然。倚枕听之。往往有能中余意者。
十二日己卯。发利川。午到昆岩。省拜坟墓。暮投庆安驿馆宿。驿本无馆。御医方震夔为督邮时所创。华洁净洒。称过客意。是夜月色垂庭。菊花弄影。孤吟不能就枕。
恕庵集卷之十一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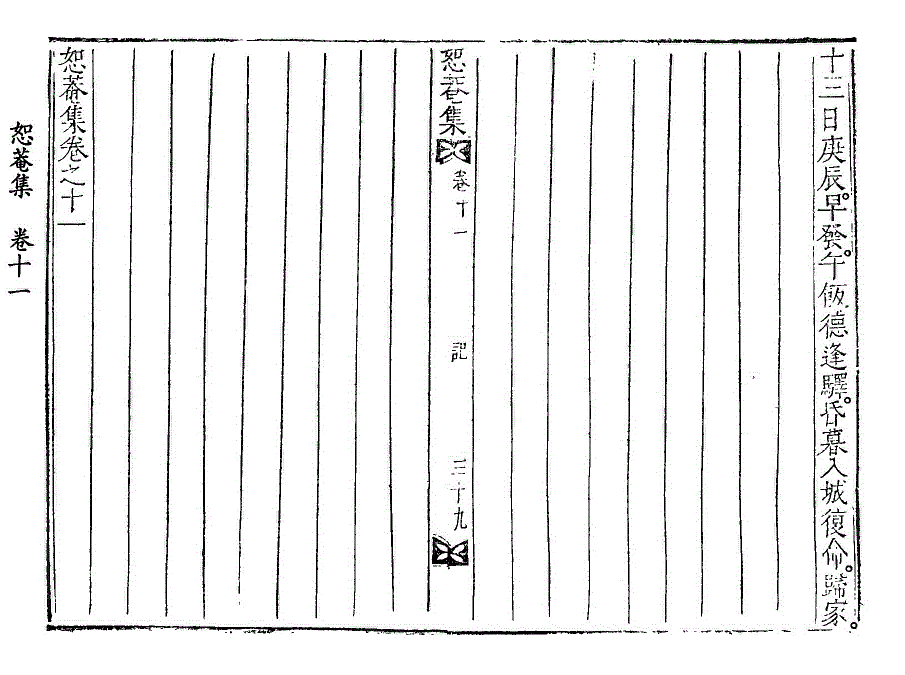 十三日庚辰。早发。午饭德逢驿。昏暮入城复命。归家。
十三日庚辰。早发。午饭德逢驿。昏暮入城复命。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