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恕庵集卷之十 第 x 页
恕庵集卷之十(平山申靖夏正甫 著)
序
序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2H 页
 送郑生来侨读书牛峡序
送郑生来侨读书牛峡序余尝见世之有志于学而贫者。往往有奔走于口腹。以不能自振而堕其业者。未始不惜其人之穷厄。而亦有以窃叹其诚之不笃也。夫贫固可忧也。而学而不能忘贫之为忧。则其所谓学之浅深。盖可见矣。故古之为学者。未闻以其贫废学。良以好学之心。能胜其恶贫之心故也。不则不足以言学也。有郑生润卿者。志于学有年矣。然顾贫甚。恐其不能有以自振而堕其业也。将弃去家事。与同学数子。读书于牛峡。以行日告余愿有言勖之。呜呼。生之志可谓勇哉。然余观其色而听其言也。悒悒然似不能忘贫之忧者。余恐生之过于忧贫而遂不能笃于为学也。生其戒之哉。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言道之急于身也如此。今生之所忧于贫者。不过口体之奉而已。甚则恶其死而已。未见其急于所谓道与学也。古之嗜学而安贫者。无过颜氏。然世之病于贫者曰。彼犹有箪食瓢饮之供也。吾之贫甚于颜氏。则安得不以动吾心哉。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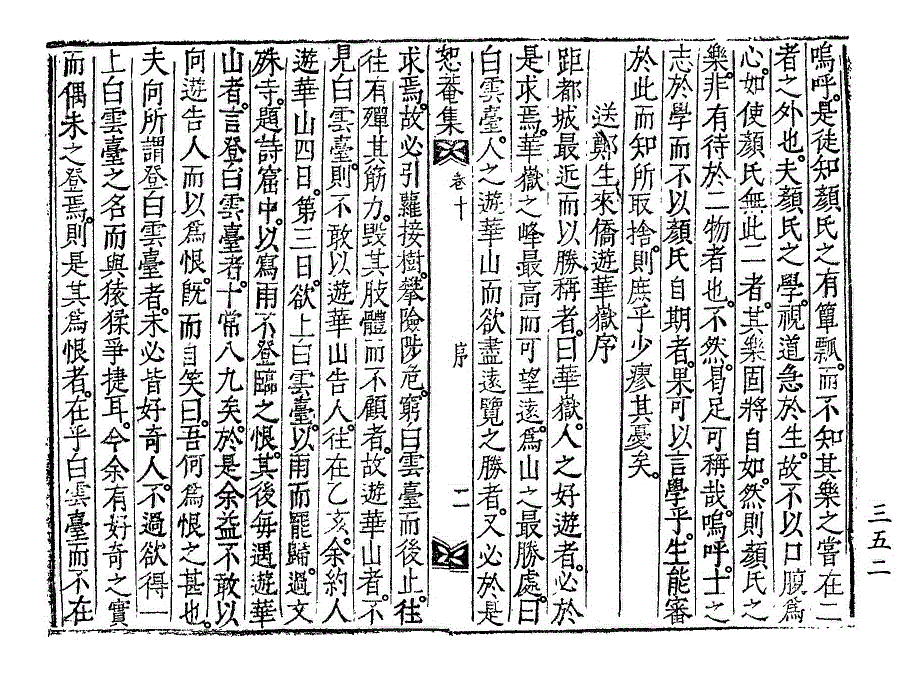 呜呼。是徒知颜氏之有箪瓢。而不知其乐之尝在二者之外也。夫颜氏之学。视道急于生。故不以口腹为心。如使颜氏无此二者。其乐固将自如。然则颜氏之乐。非有待于二物者也。不然。曷足可称哉。呜呼。士之志于学而不以颜氏自期者。果可以言学乎。生能审于此而知所取舍。则庶乎少瘳其忧矣。
呜呼。是徒知颜氏之有箪瓢。而不知其乐之尝在二者之外也。夫颜氏之学。视道急于生。故不以口腹为心。如使颜氏无此二者。其乐固将自如。然则颜氏之乐。非有待于二物者也。不然。曷足可称哉。呜呼。士之志于学而不以颜氏自期者。果可以言学乎。生能审于此而知所取舍。则庶乎少瘳其忧矣。送郑生来侨游华岳序
距都城最近而以胜称者。曰华岳。人之好游者。必于是求焉。华岳之峰最高而可望远。为山之最胜处。曰白云台。人之游华山而欲尽远览之胜者。又必于是求焉。故必引萝接树。攀险陟危。穷白云台而后止。往往有殚其筋力。毁其肢体而不顾者。故游华山者。不见白云台。则不敢以游华山告人。往在乙亥。余约人游华山四日。第三日。欲上白云台。以雨而罢归。过文殊寺。题诗窟中。以写雨不登临之恨。其后每遇游华山者。言登白云台者。十常八九矣。于是余益不敢以向游告人而以为恨。既而自笑曰。吾何为恨之甚也。夫向所谓登白云台者。未必皆好奇人。不过欲得一上白云台之名而与猿猱争捷耳。今余有好奇之实而偶未之登焉。则是其为恨者。在乎白云台而不在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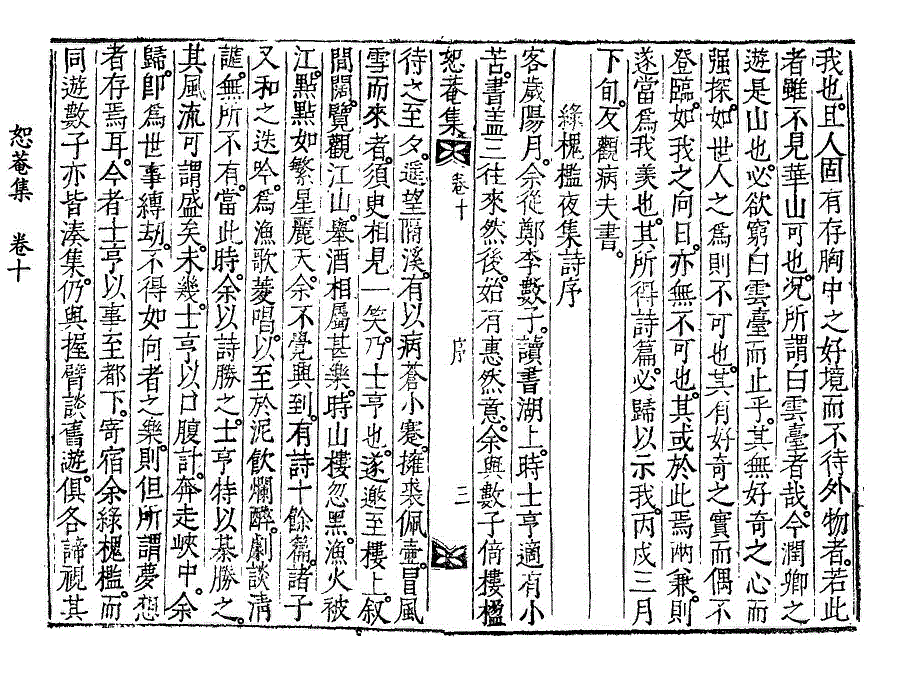 我也。且人固有存胸中之好境而不待外物者。若此者虽不见华山可也。况所谓白云台者哉。今润卿之游是山也。必欲穷白云台而止乎。其无好奇之心而强探。如世人之为则不可也。其有好奇之实而偶不登临。如我之向日。亦无不可也。其或于此焉两兼。则遂当为我羡也。其所得诗篇。必归以示我。丙戌三月下旬。反观病夫书。
我也。且人固有存胸中之好境而不待外物者。若此者虽不见华山可也。况所谓白云台者哉。今润卿之游是山也。必欲穷白云台而止乎。其无好奇之心而强探。如世人之为则不可也。其有好奇之实而偶不登临。如我之向日。亦无不可也。其或于此焉两兼。则遂当为我羡也。其所得诗篇。必归以示我。丙戌三月下旬。反观病夫书。绿槐槛夜集诗序
客岁阳月。余从郑李数子。读书湖上。时士亨适有小苦。书盖三往来然后。始有惠然意。余与数子倚楼楹待之至夕。遥望隔溪。有以病苍小蹇。拥裘佩壶。冒风雪而来者。须臾相见一笑。乃士亨也。遂邀至楼上。叙间阔。览观江山。举酒相属甚乐。时山楼忽黑。渔火被江。点点如繁星丽天。余不觉兴到。有诗十馀篇。诸子又和之迭吟。为渔歌菱唱。以至于泥饮烂醉。剧谈清谑。无所不有。当此时。余以诗胜之。士亨特以棋胜之。其风流可谓盛矣。未几。士亨以口腹计。奔走峡中。余归。即为世事缚劫。不得如向者之乐。则但所谓梦想者存焉耳。今者士亨以事至都下。寄宿余绿槐槛。而同游数子亦皆凑集。仍与握臂谈旧游。俱各谛视其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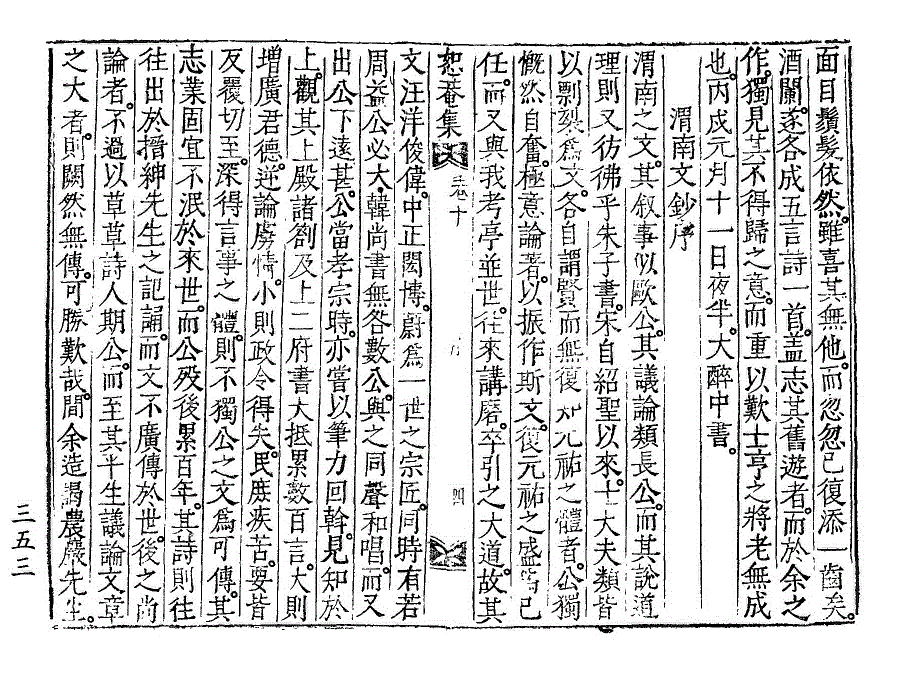 面目须发依然。虽喜其无他。而忽忽已复添一齿矣。酒阑。遂各成五言诗一首。盖志其旧游者。而于余之作。独见其不得归之意。而重以叹士亨之将老无成也。丙戌元月十一日夜半。大醉中书。
面目须发依然。虽喜其无他。而忽忽已复添一齿矣。酒阑。遂各成五言诗一首。盖志其旧游者。而于余之作。独见其不得归之意。而重以叹士亨之将老无成也。丙戌元月十一日夜半。大醉中书。渭南文钞序
渭南之文。其叙事似欧公。其议论类长公。而其说道理则又彷佛乎朱子书。宋自绍圣以来。士大夫类皆以剽裂为文。各自谓贤而无复知元祐之体者。公独慨然自奋。极意论著。以振作斯文。复元祐之盛为己任。而又与我考亭并世。往来讲磨。卒引之大道。故其文汪洋俊伟。中正闳博。蔚为一世之宗匠。同时有若周益公必大,韩尚书无咎数公。与之同声和唱。而又出公下远甚。公当孝宗时。亦尝以笔力回斡。见知于上。观其上殿诸劄及上二府书大抵累数百言。大则增广君德。逆论虏情。小则政令得失。民庶疾苦。要皆反覆切至。深得言事之体。则不独公之文为可传。其志业固宜不泯于来世。而公殁后累百年。其诗则往往出于搢绅先生之记诵。而文不广传于世。后之尚论者。不过以草草诗人期公。而至其平生议论文章之大者。则阙然无传。可胜叹哉。间余造谒农岩先生。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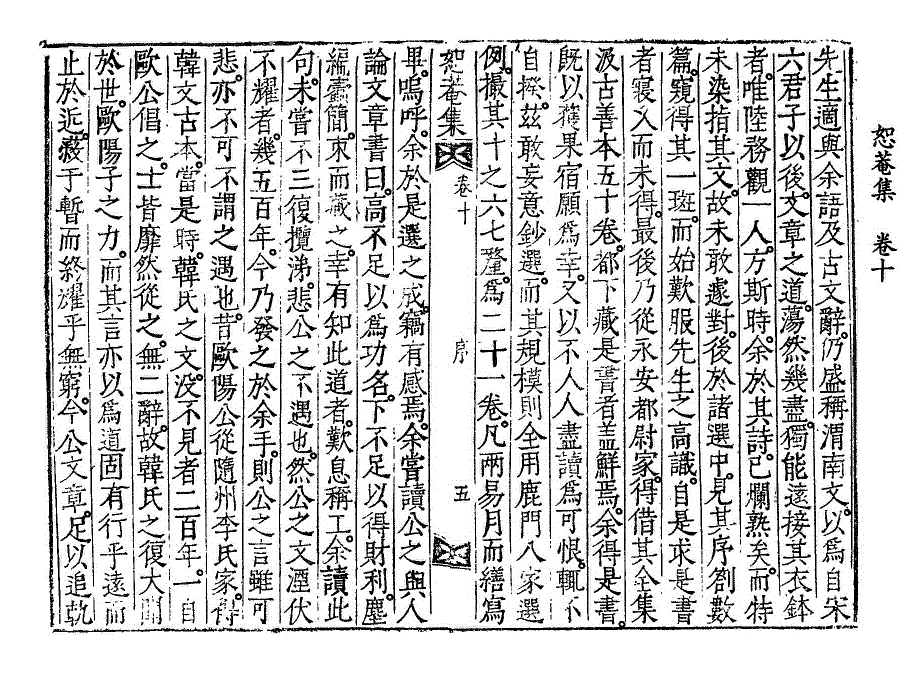 先生适与余语及古文辞。仍盛称渭南文。以为自宋六君子以后。文章之道。荡然几尽。独能远接其衣钵者。唯陆务观一人。方斯时。余于其诗。已烂熟矣。而特未染指其文。故未敢遽对。后于诸选中。见其序劄数篇。窥得其一斑。而始叹服先生之高识。自是求是书者寝久而未得。最后乃从永安都尉家。得借其全集汲古善本五十卷。都下藏是书者盖鲜焉。余得是书。既以获果宿愿为幸。又以不人人尽读为可恨。辄不自揆。玆敢妄意钞选。而其规模则全用鹿门八家选例。撮其十之六七釐。为二十一卷。凡两易月而缮写毕。呜呼。余于是选之成。窃有感焉。余尝读公之与人论文章书曰。高不足以为功名。下不足以得财利。尘编蠹简。束而藏之。幸有知此道者。叹息称工。余读此句。未尝不三复揽涕。悲公之不遇也。然公之文湮伏不耀者。几五百年。今乃发之于余手。则公之言虽可悲。亦不可不谓之遇也。昔欧阳公从随州李氏家。得韩文古本。当是时。韩氏之文。没不见者二百年。一自欧公倡之。士皆靡然从之。无二辞。故韩氏之复大闻于世。欧阳子之力。而其言亦以为道固有行乎远而止于近。蔽于暂而终耀乎无穷。今公文章。足以追轨
先生适与余语及古文辞。仍盛称渭南文。以为自宋六君子以后。文章之道。荡然几尽。独能远接其衣钵者。唯陆务观一人。方斯时。余于其诗。已烂熟矣。而特未染指其文。故未敢遽对。后于诸选中。见其序劄数篇。窥得其一斑。而始叹服先生之高识。自是求是书者寝久而未得。最后乃从永安都尉家。得借其全集汲古善本五十卷。都下藏是书者盖鲜焉。余得是书。既以获果宿愿为幸。又以不人人尽读为可恨。辄不自揆。玆敢妄意钞选。而其规模则全用鹿门八家选例。撮其十之六七釐。为二十一卷。凡两易月而缮写毕。呜呼。余于是选之成。窃有感焉。余尝读公之与人论文章书曰。高不足以为功名。下不足以得财利。尘编蠹简。束而藏之。幸有知此道者。叹息称工。余读此句。未尝不三复揽涕。悲公之不遇也。然公之文湮伏不耀者。几五百年。今乃发之于余手。则公之言虽可悲。亦不可不谓之遇也。昔欧阳公从随州李氏家。得韩文古本。当是时。韩氏之文。没不见者二百年。一自欧公倡之。士皆靡然从之。无二辞。故韩氏之复大闻于世。欧阳子之力。而其言亦以为道固有行乎远而止于近。蔽于暂而终耀乎无穷。今公文章。足以追轨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4L 页
 韩氏。则其言之传。自当与天壤俱弊。岂非欧公所谓终耀乎无穷者。而顾余之自视缺然者。固不足以望欧公万一。则公之文章。又奚足待余而轻重哉。然其笃于慕古嗜文。则自谓庶几无愧乎欧公。言之为轻为重。姑未暇论。世之读是选者。倘以是恕其僭妄则幸矣。
韩氏。则其言之传。自当与天壤俱弊。岂非欧公所谓终耀乎无穷者。而顾余之自视缺然者。固不足以望欧公万一。则公之文章。又奚足待余而轻重哉。然其笃于慕古嗜文。则自谓庶几无愧乎欧公。言之为轻为重。姑未暇论。世之读是选者。倘以是恕其僭妄则幸矣。赠郑生来侨序
委巷士之以诗名世而从吾游者有三人焉。曰沧浪洪道长,郑惠卿,郑润卿。三人之中。老者沧浪。少者二郑。而润卿独于余为同齿。余之知三子也。润卿为最先。沧浪惠卿其次也。三子之从余游。俱以其诗。而于余之诗。其称沧浪惠卿者。居十二三。而其称润卿者。则独居十四五。其交也旧。故其情也特厚。其情也厚。故其见于诗也为多。呜呼。余于三子者。亦见其难舍。而其于润卿。尤为亲好。则又不待言说矣。既而沧浪西惠卿东。各为世故所疲。而润卿素多病。闻昌城出药水泉。可以疗己疾。又闻其往来。多楼观山水之胜。欲因之一游。将赢粮买乘。为西关千里役。自余之与三子者游。盖未尝一日离。而今乃相继告别于半月之内。呜呼。聚散之无常。其亦悲矣。虽然。余于三子之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5H 页
 行。尤有以自伤者。今自他人观余与三子者。则余为达而三子则穷也。余为伸而三子则屈也。余为处而三子则行也。余为逸而三子则劳也。以达与伸而言穷屈。以处与逸而言行劳。则孰不以我为可贺而以三子者为可唁也。然余与三子者之好文章而薄禄位则同也。今三子者。虽有远游之叹。而有山水登览之胜焉。有歌诗啸咏之兴焉。夫是数者之乐。无替于前。而独余牛马其身。逐逐于风埃中。龌龊为名缰之役。于其山水文章之所尝好者。十无其一焉。则余之所得者。既未足为三子者羡。而其所失者。已足为三子者悲也。由玆而言。余则不保其乐。而三子者则能保焉。余则有变。而三子者则不变焉。夫以乐悯不乐。以无变嗟变者。人情之常也。吾未知三子者悲余乎。余悲三子乎。余于三子者之去。均有所感。而润卿于余为最好。故特发之于润卿也。丙戌仲秋下旬。反观病夫书。
行。尤有以自伤者。今自他人观余与三子者。则余为达而三子则穷也。余为伸而三子则屈也。余为处而三子则行也。余为逸而三子则劳也。以达与伸而言穷屈。以处与逸而言行劳。则孰不以我为可贺而以三子者为可唁也。然余与三子者之好文章而薄禄位则同也。今三子者。虽有远游之叹。而有山水登览之胜焉。有歌诗啸咏之兴焉。夫是数者之乐。无替于前。而独余牛马其身。逐逐于风埃中。龌龊为名缰之役。于其山水文章之所尝好者。十无其一焉。则余之所得者。既未足为三子者羡。而其所失者。已足为三子者悲也。由玆而言。余则不保其乐。而三子者则能保焉。余则有变。而三子者则不变焉。夫以乐悯不乐。以无变嗟变者。人情之常也。吾未知三子者悲余乎。余悲三子乎。余于三子者之去。均有所感。而润卿于余为最好。故特发之于润卿也。丙戌仲秋下旬。反观病夫书。送家侄昉游枫岳序
家侄之游金刚也。书来史局以报余曰。侄之行已有日矣。以侄平生之善病。不能游近都山水。而今幸得金刚之远且胜而以为之游。中心固已有自幸者矣。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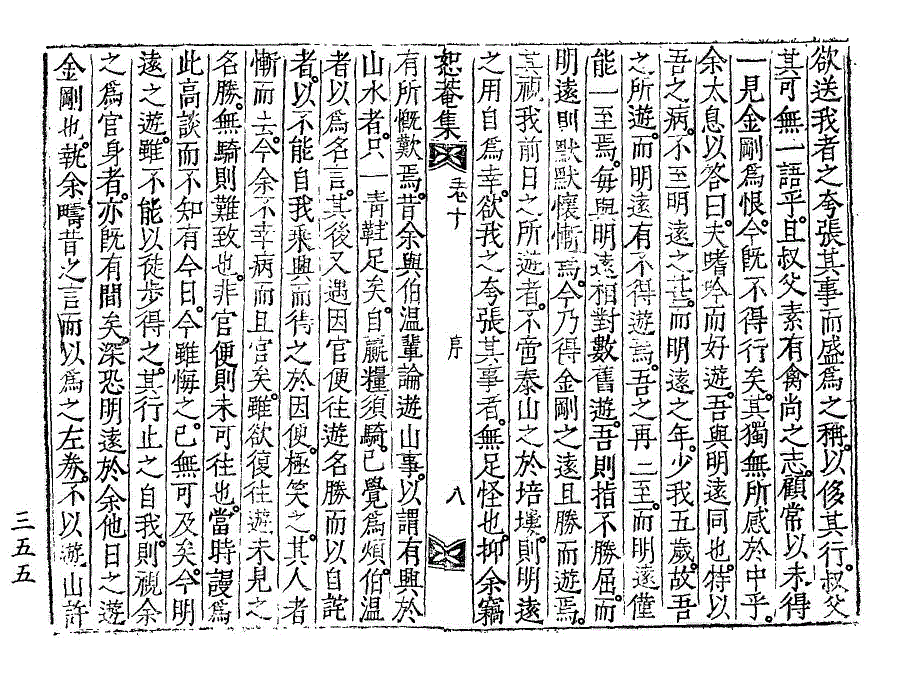 欲送我者之夸张其事而盛为之称。以侈其行。叔父其可无一语乎。且叔父素有禽尚之志。顾常以未得一见金刚为恨。今既不得行矣。其独无所感于中乎。余太息以答曰。夫嗜吟而好游。吾与明远同也。特以吾之病。不至明远之甚。而明远之年。少我五岁。故吾之所游。而明远有不得游焉。吾之再三至。而明远仅能一至焉。每与明远相对数旧游。吾则指不胜屈。而明远则默默怀惭焉。今乃得金刚之远且胜而游焉。其视我前日之所游者。不啻泰山之于培塿。则明远之用自为幸。欲我之夸张其事者。无足怪也。抑余窃有所慨叹焉。昔余与伯温辈论游山事。以谓有兴于山水者。只一青鞋足矣。自赢粮须骑。已觉为烦。伯温者以为名言。其后又遇因官便往游名胜而以自诧者。以不能自我乘兴而得之于因便。极笑之。其人者惭而去。今余不幸病而且官矣。虽欲复往游未见之名胜。无骑则难致也。非官便则未可往也。当时谩为此高谈而不知有今日。今虽悔之。已无可及矣。今明远之游。虽不能以徒步得之。其行止之自我。则视余之为官身者。亦既有间矣。深恐明远于余他日之游金刚也。执余畴昔之言而以为之左券。不以游山许
欲送我者之夸张其事而盛为之称。以侈其行。叔父其可无一语乎。且叔父素有禽尚之志。顾常以未得一见金刚为恨。今既不得行矣。其独无所感于中乎。余太息以答曰。夫嗜吟而好游。吾与明远同也。特以吾之病。不至明远之甚。而明远之年。少我五岁。故吾之所游。而明远有不得游焉。吾之再三至。而明远仅能一至焉。每与明远相对数旧游。吾则指不胜屈。而明远则默默怀惭焉。今乃得金刚之远且胜而游焉。其视我前日之所游者。不啻泰山之于培塿。则明远之用自为幸。欲我之夸张其事者。无足怪也。抑余窃有所慨叹焉。昔余与伯温辈论游山事。以谓有兴于山水者。只一青鞋足矣。自赢粮须骑。已觉为烦。伯温者以为名言。其后又遇因官便往游名胜而以自诧者。以不能自我乘兴而得之于因便。极笑之。其人者惭而去。今余不幸病而且官矣。虽欲复往游未见之名胜。无骑则难致也。非官便则未可往也。当时谩为此高谈而不知有今日。今虽悔之。已无可及矣。今明远之游。虽不能以徒步得之。其行止之自我。则视余之为官身者。亦既有间矣。深恐明远于余他日之游金刚也。执余畴昔之言而以为之左券。不以游山许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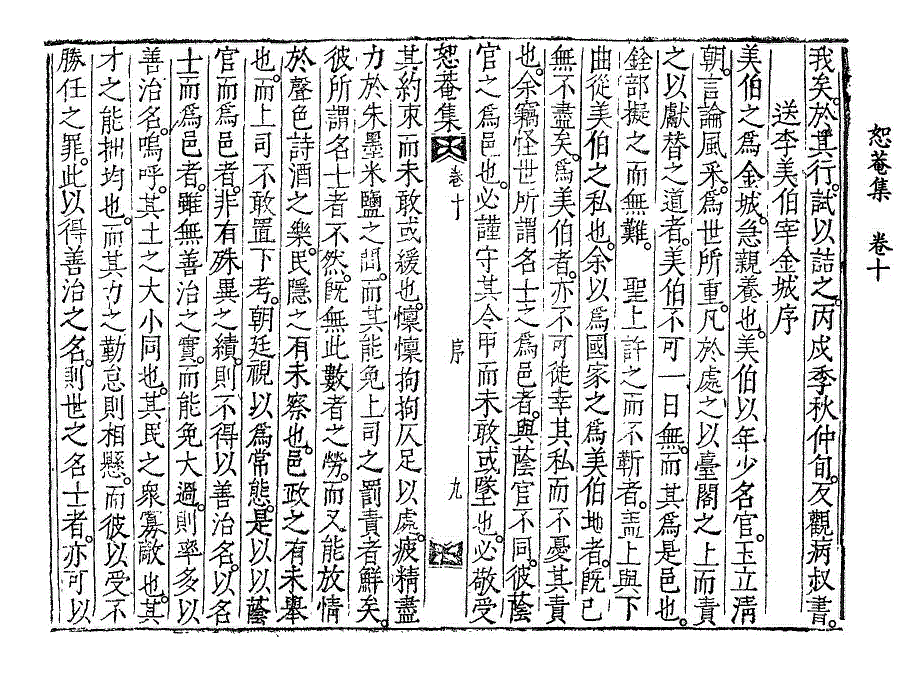 我矣。于其行。试以诘之。丙戌季秋仲旬。反观病叔书。
我矣。于其行。试以诘之。丙戌季秋仲旬。反观病叔书。送李美伯宰金城序
美伯之为金城。急亲养也。美伯以年少名官。玉立清朝。言论风采。为世所重。凡于处之以台阁之上而责之以献替之道者。美伯不可一日无。而其为是邑也。铨部拟之而无难。 圣上许之而不靳者。盖上与下曲从美伯之私也。余以为国家之为美伯地者。既已无不尽矣。为美伯者。亦不可徒幸其私而不忧其责也。余窃怪世所谓名士之为邑者。与荫官不同。彼荫官之为邑也。必谨守其令甲而未敢或坠也。必敬受其约束而未敢或缓也。懔懔拘拘仄足以处。疲精尽力于朱墨米盐之间。而其能免上司之罚责者鲜矣。彼所谓名士者不然。既无此数者之劳。而又能放情于声色诗酒之乐。民隐之有未察也。邑政之有未举也。而上司不敢置下考。朝廷视以为常态。是以以荫官而为邑者。非有殊异之绩。则不得以善治名。以名士而为邑者。虽无善治之实。而能免大过。则率多以善治名。呜呼。其土之大小同也。其民之众寡敌也。其才之能拙均也。而其力之勤怠则相悬。而彼以受不胜任之罪。此以得善治之名。则世之名士者。亦可以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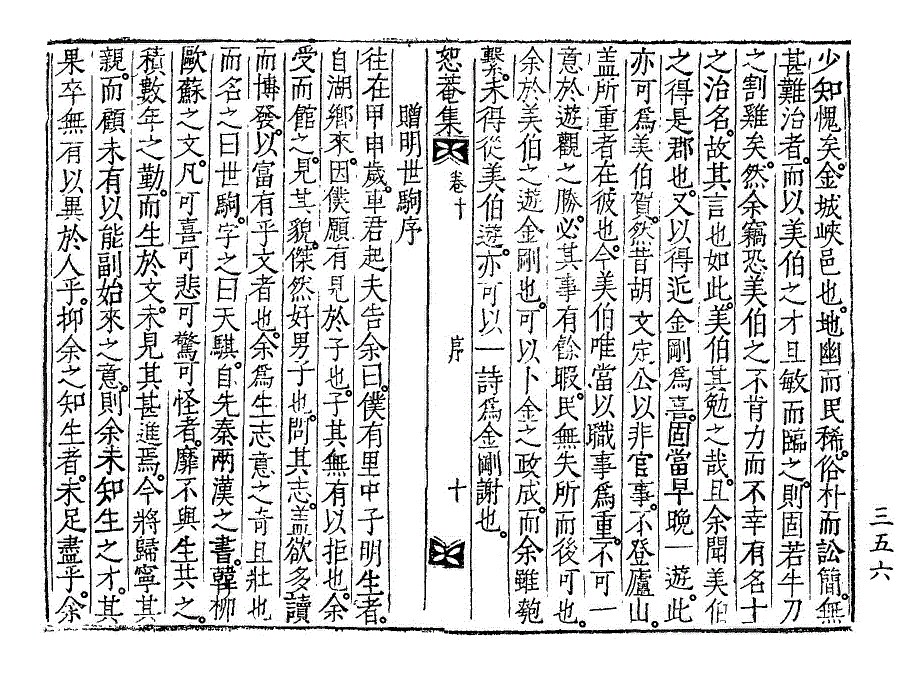 少知愧矣。金城峡邑也。地幽而民稀。俗朴而讼简。无甚难治者。而以美伯之才且敏而临之。则固若牛刀之割鸡矣。然余窃恐美伯之不肯力而不幸有名士之治名。故其言也如此。美伯其勉之哉。且余闻美伯之得是郡也。又以得近金刚为喜。固当早晚一游。此亦可为美伯贺。然昔胡文定公以非官事。不登庐山。盖所重者在彼也。今美伯唯当以职事为重。不可一意于游观之胜。必其事有馀暇。民无失所而后可也。余于美伯之游金刚也。可以卜金之政成。而余虽匏系。未得从美伯游。亦可以一诗为金刚谢也。
少知愧矣。金城峡邑也。地幽而民稀。俗朴而讼简。无甚难治者。而以美伯之才且敏而临之。则固若牛刀之割鸡矣。然余窃恐美伯之不肯力而不幸有名士之治名。故其言也如此。美伯其勉之哉。且余闻美伯之得是郡也。又以得近金刚为喜。固当早晚一游。此亦可为美伯贺。然昔胡文定公以非官事。不登庐山。盖所重者在彼也。今美伯唯当以职事为重。不可一意于游观之胜。必其事有馀暇。民无失所而后可也。余于美伯之游金刚也。可以卜金之政成。而余虽匏系。未得从美伯游。亦可以一诗为金刚谢也。赠明世驹序
往在甲申岁。车君起夫告余曰。仆有里中子明生者。自湖乡来。因仆愿有见于子也。子其无有以拒也。余受而馆之。见其貌。杰然好男子也。问其志。盖欲多读而博发。以富有乎文者也。余为生志意之奇且壮也而名之曰世驹。字之曰天骐。自先秦两汉之书。韩柳欧苏之文。凡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靡不与生共之。积数年之勤。而生于文。未见其甚进焉。今将归宁其亲。而顾未有以能副始来之意。则余未知生之才。其果卒无有以异于人乎。抑余之知生者。未足尽乎。余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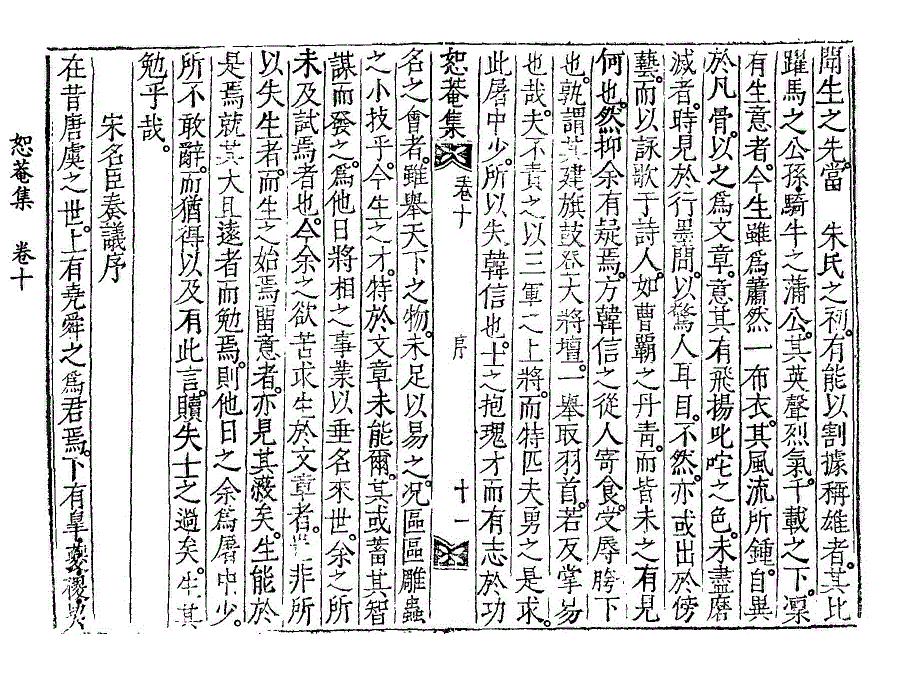 闻生之先。当 朱氏之初。有能以割据称雄者。其比跃马之公孙,骑牛之蒲公。其英声烈气。千载之下。凛有生意者。今生虽为萧然一布衣。其风流所钟。自异于凡骨。以之为文章。意其有飞扬叱咜之色。未尽磨灭者。时见于行墨间。以惊人耳目。不然。亦或出于傍艺。而以咏歌于诗人。如曹霸之丹青。而皆未之有见何也。然抑余有疑焉。方韩信之从人寄食。受辱胯下也。孰谓其建旗鼓登大将坛。一举取羽首。若反掌易也哉。夫不责之以三军之上将。而特匹夫勇之是求。此屠中少。所以失韩信也。士之抱瑰才而有志于功名之会者。虽举天下之物。未足以易之。况区区雕虫之小技乎。今生之才。特于文章未能尔。其或蓄其智谋而发之。为他日将相之事业以垂名来世。余之所未及试焉者也。今余之欲苦求生于文章者。岂非所以失生者。而生之始焉留意者。亦见其蔽矣。生能于是焉就其大且远者而勉焉。则他日之余为屠中少。所不敢辞。而犹得以及有此言。赎失士之过矣。生其勉乎哉。
闻生之先。当 朱氏之初。有能以割据称雄者。其比跃马之公孙,骑牛之蒲公。其英声烈气。千载之下。凛有生意者。今生虽为萧然一布衣。其风流所钟。自异于凡骨。以之为文章。意其有飞扬叱咜之色。未尽磨灭者。时见于行墨间。以惊人耳目。不然。亦或出于傍艺。而以咏歌于诗人。如曹霸之丹青。而皆未之有见何也。然抑余有疑焉。方韩信之从人寄食。受辱胯下也。孰谓其建旗鼓登大将坛。一举取羽首。若反掌易也哉。夫不责之以三军之上将。而特匹夫勇之是求。此屠中少。所以失韩信也。士之抱瑰才而有志于功名之会者。虽举天下之物。未足以易之。况区区雕虫之小技乎。今生之才。特于文章未能尔。其或蓄其智谋而发之。为他日将相之事业以垂名来世。余之所未及试焉者也。今余之欲苦求生于文章者。岂非所以失生者。而生之始焉留意者。亦见其蔽矣。生能于是焉就其大且远者而勉焉。则他日之余为屠中少。所不敢辞。而犹得以及有此言。赎失士之过矣。生其勉乎哉。宋名臣奏议序
在昔唐虞之世。上有尧舜之为君焉。下有皋,夔,稷,契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7L 页
 之为臣焉。其以行道也。如天之运。而其以承奉也。如四时之行焉。都俞吁咈而至道凝焉。恭己无为而治化成焉。当斯时也。上无违度之失。则下无有以规之也。上无败谋之忧。则下无有以救之也。上而无蔽于听察。则下而无事于补聪也。上而无疑于取舍。则下而无事于赞决也。盖唐虞之世。几乎忘言矣。而况夫笔之于书者乎。虽然。舜之命禹之辞曰。嘉言罔攸伏。是则舜未尝不急于言也。禹之戒舜之辞曰。无若丹朱傲。是则禹未尝忘戒于舜也。夫不以自足于吾心而犹有待于人言。不以其君之已圣而有不肖子之恐。此舜禹之朝廷。不至多言而治也。至若伊尹之于太甲。明言烈祖之成德。周公之于成王。告以君子之无逸。几各累百言。其为情恳苦而多感。其为辞谆切而易明。此盖由于两君之德。不及于尧舜之圣。故二公之为臣。不能如皋夔之简默则其势然也。降及叔季。时君世主。寝失其德。诤臣拂士。争起而救之。远而说天道。近而言人事。大而论君上之心术。小而陈政令之失得。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其口。宣之于口而笔之于其书。不幸而其君之不省。则言亦不可止而有重言而复言也。于是乎奏疏之不能一日以无。而治
之为臣焉。其以行道也。如天之运。而其以承奉也。如四时之行焉。都俞吁咈而至道凝焉。恭己无为而治化成焉。当斯时也。上无违度之失。则下无有以规之也。上无败谋之忧。则下无有以救之也。上而无蔽于听察。则下而无事于补聪也。上而无疑于取舍。则下而无事于赞决也。盖唐虞之世。几乎忘言矣。而况夫笔之于书者乎。虽然。舜之命禹之辞曰。嘉言罔攸伏。是则舜未尝不急于言也。禹之戒舜之辞曰。无若丹朱傲。是则禹未尝忘戒于舜也。夫不以自足于吾心而犹有待于人言。不以其君之已圣而有不肖子之恐。此舜禹之朝廷。不至多言而治也。至若伊尹之于太甲。明言烈祖之成德。周公之于成王。告以君子之无逸。几各累百言。其为情恳苦而多感。其为辞谆切而易明。此盖由于两君之德。不及于尧舜之圣。故二公之为臣。不能如皋夔之简默则其势然也。降及叔季。时君世主。寝失其德。诤臣拂士。争起而救之。远而说天道。近而言人事。大而论君上之心术。小而陈政令之失得。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其口。宣之于口而笔之于其书。不幸而其君之不省。则言亦不可止而有重言而复言也。于是乎奏疏之不能一日以无。而治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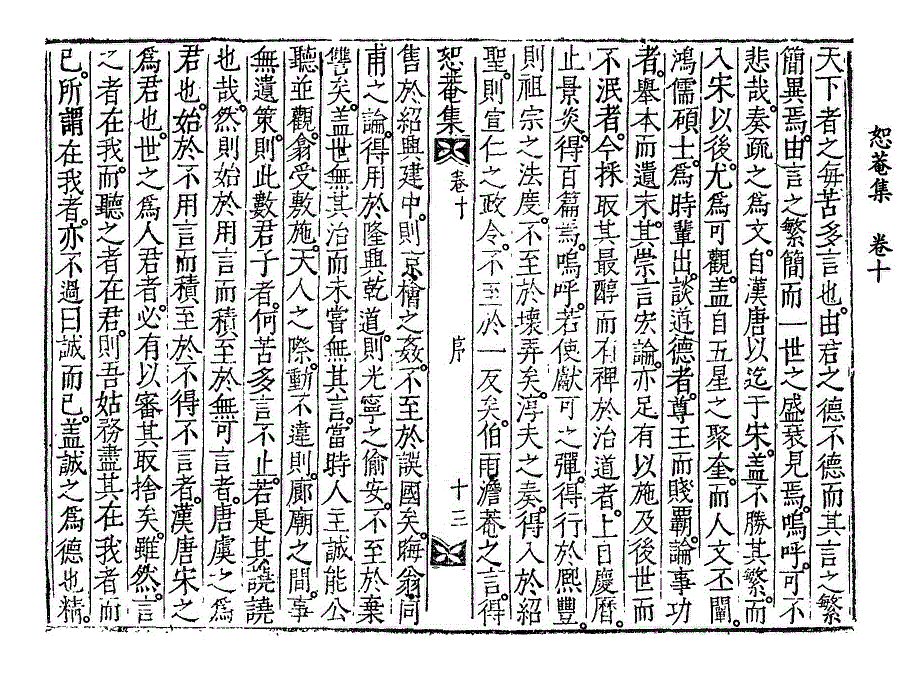 天下者之每苦多言也。由君之德不德而其言之繁简异焉。由言之繁简而一世之盛衰见焉。呜呼。可不悲哉。奏疏之为文。自汉唐以迄于宋。盖不胜其繁。而入宋以后。尤为可观。盖自五星之聚奎。而人文丕阐。鸿儒硕士。为时辈出。谈道德者。尊王而贱霸。论事功者。举本而遗末。其崇言宏论。亦足有以施及后世而不泯者。今采取其最醇而有裨于治道者。上自庆历。止景炎。得百篇焉。呜呼。若使献可之弹。得行于熙丰。则祖宗之法度。不至于坏弄矣。淳夫之奏。得入于绍圣。则宣仁之政令。不至于一反矣。伯雨,澹庵之言。得售于绍兴建中。则京,桧之奸。不至于误国矣。晦翁,同甫之论。得用于隆兴乾道。则光宁之偷安。不至于弃雠矣。盖世无其治而未尝无其言。当时人主诚能公听并观。翕受敷施。天人之际。动不违则。廊庙之间。事无遗策。则此数君子者。何苦多言不止。若是其譊譊也哉。然则始于用言而积至于无可言者。唐虞之为君也。始于不用言而积至于不得不言者。汉唐宋之为君也。世之为人君者。必有以审其取舍矣。虽然。言之者在我。而听之者在君。则吾姑务尽其在我者而已。所谓在我者。亦不过曰诚而已。盖诚之为德也精。
天下者之每苦多言也。由君之德不德而其言之繁简异焉。由言之繁简而一世之盛衰见焉。呜呼。可不悲哉。奏疏之为文。自汉唐以迄于宋。盖不胜其繁。而入宋以后。尤为可观。盖自五星之聚奎。而人文丕阐。鸿儒硕士。为时辈出。谈道德者。尊王而贱霸。论事功者。举本而遗末。其崇言宏论。亦足有以施及后世而不泯者。今采取其最醇而有裨于治道者。上自庆历。止景炎。得百篇焉。呜呼。若使献可之弹。得行于熙丰。则祖宗之法度。不至于坏弄矣。淳夫之奏。得入于绍圣。则宣仁之政令。不至于一反矣。伯雨,澹庵之言。得售于绍兴建中。则京,桧之奸。不至于误国矣。晦翁,同甫之论。得用于隆兴乾道。则光宁之偷安。不至于弃雠矣。盖世无其治而未尝无其言。当时人主诚能公听并观。翕受敷施。天人之际。动不违则。廊庙之间。事无遗策。则此数君子者。何苦多言不止。若是其譊譊也哉。然则始于用言而积至于无可言者。唐虞之为君也。始于不用言而积至于不得不言者。汉唐宋之为君也。世之为人君者。必有以审其取舍矣。虽然。言之者在我。而听之者在君。则吾姑务尽其在我者而已。所谓在我者。亦不过曰诚而已。盖诚之为德也精。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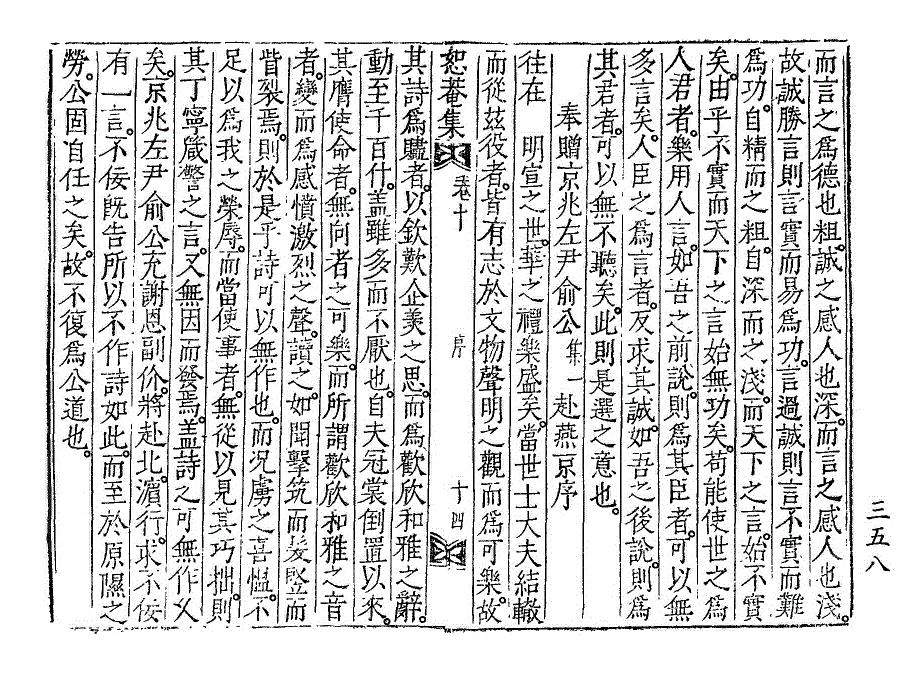 而言之为德也粗。诚之感人也深。而言之感人也浅。故诚胜言则言实而易为功。言过诚则言不实而难为功。自精而之粗。自深而之浅。而天下之言。始不实矣。由乎不实而天下之言始无功矣。苟能使世之为人君者。乐用人言。如吾之前说。则为其臣者。可以无多言矣。人臣之为言者。反求其诚。如吾之后说。则为其君者。可以无不听矣。此则是选之意也。
而言之为德也粗。诚之感人也深。而言之感人也浅。故诚胜言则言实而易为功。言过诚则言不实而难为功。自精而之粗。自深而之浅。而天下之言。始不实矣。由乎不实而天下之言始无功矣。苟能使世之为人君者。乐用人言。如吾之前说。则为其臣者。可以无多言矣。人臣之为言者。反求其诚。如吾之后说。则为其君者。可以无不听矣。此则是选之意也。奉赠京兆左尹俞公(集一)赴燕京序
往在 明宣之世。华之礼乐盛矣。当世士大夫结辙而从玆役者。皆有志于文物声明之观而为可乐。故其诗为赆者。以钦叹企羡之思。而为欢欣和雅之辞。动至千百什。盖虽多而不厌也。自夫冠裳倒置以来。其膺使命者。无向者之可乐。而所谓欢欣和雅之音者。变而为感愤激烈之声。读之。如闻击筑而发竖而眦裂焉。则于是乎诗可以无作也。而况虏之喜愠。不足以为我之荣辱。而当使事者。无从以见其巧拙。则其丁宁箴警之言。又无因而发焉。盖诗之可无作久矣。京兆左尹俞公充谢恩副价。将赴北。滨行。求不佞有一言。不佞既告所以不作诗如此。而至于原隰之劳。公固自任之矣。故不复为公道也。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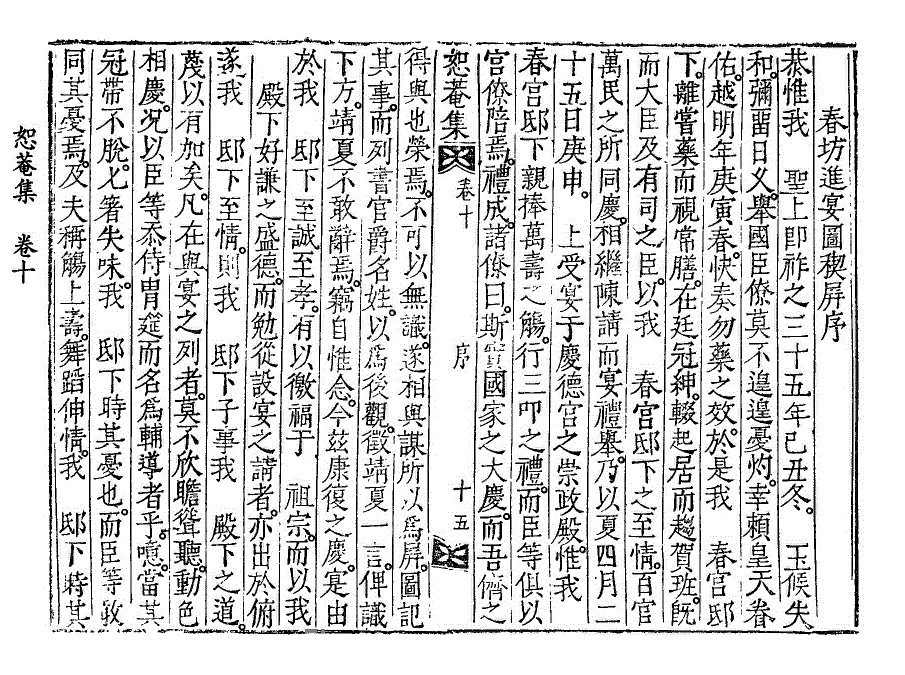 春坊进宴图稧屏序
春坊进宴图稧屏序恭惟我 圣上即祚之三十五年己丑冬。 玉候失和。弥留日久。举国臣僚莫不遑遑忧灼。幸赖皇天眷佑。越明年庚寅春。快奏勿药之效。于是我 春宫邸下。离尝药而视常膳。在廷冠绅。辍起居而趋贺班。既而大臣及有司之臣。以我 春宫邸下之至情。百官万民之所同庆。相继陈请而宴礼举。乃以夏四月二十五日庚申。 上受宴于庆德宫之崇政殿。惟我 春宫邸下亲捧万寿之觞。行三叩之礼。而臣等俱以宫僚陪焉。礼成。诸僚曰。斯实国家之大庆。而吾侪之得与也荣焉。不可以无识。遂相与谋所以为屏。图记其事。而列书官爵名姓。以为后观。徵靖夏一言。俾识下方。靖夏不敢辞焉。窃自惟念。今玆康复之庆。寔由于我 邸下至诚至孝。有以徼福于 祖宗。而以我 殿下好谦之盛德。而勉从设宴之请者。亦出于俯遂我 邸下至情。则我 邸下子事我 殿下之道。蔑以有加矣。凡在与宴之列者。莫不欣瞻耸听。动色相庆。况以臣等忝侍胄筵而名为辅导者乎。噫。当其冠带不脱。匕箸失味。我 邸下时其忧也。而臣等敢同其忧焉。及夫称觞上寿。舞蹈伸情。我 邸下时其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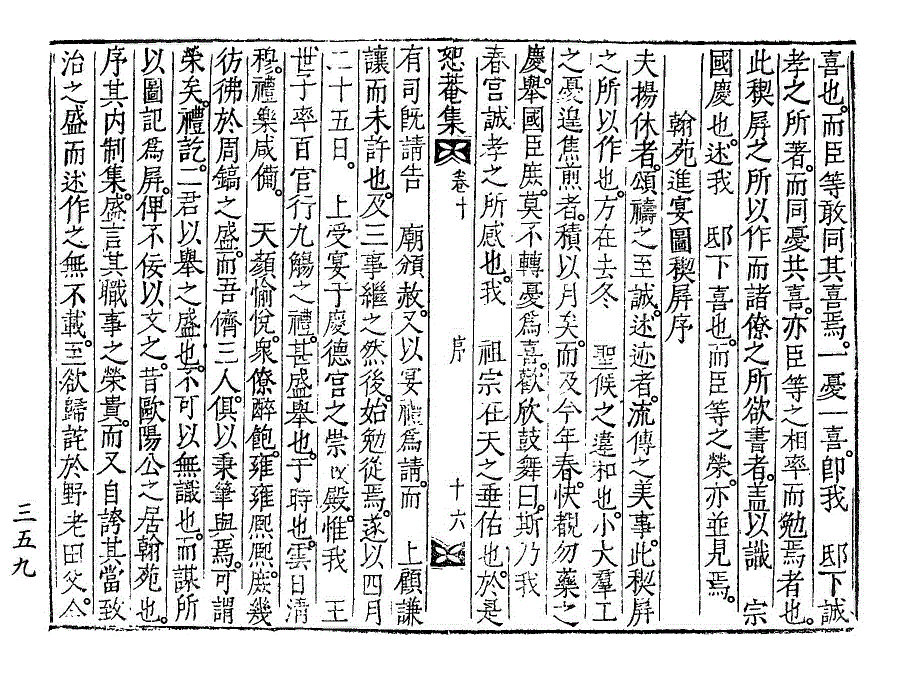 喜也。而臣等敢同其喜焉。一忧一喜。即我 邸下诚孝之所著。而同忧共喜。亦臣等之相率而勉焉者也。此稧屏之所以作而诸僚之所欲书者。盖以识 宗国庆也。述我 邸下喜也。而臣等之荣。亦并见焉。
喜也。而臣等敢同其喜焉。一忧一喜。即我 邸下诚孝之所著。而同忧共喜。亦臣等之相率而勉焉者也。此稧屏之所以作而诸僚之所欲书者。盖以识 宗国庆也。述我 邸下喜也。而臣等之荣。亦并见焉。翰苑进宴图稧屏序
夫扬休者。颂祷之至诚。述迹者。流传之美事。此稧屏之所以作也。方在去冬 圣候之违和也。小大群工之忧遑焦煎者。积以月矣。而及今年春。快睹勿药之庆。举国臣庶。莫不转忧为喜。欢欣鼓舞曰。斯乃我 春宫诚孝之所感也。我 祖宗在天之垂佑也。于是有司既请告 庙颁赦。又以宴礼为请。而 上顾谦让而未许也。及三事继之然后。始勉从焉。遂以四月二十五日。 上受宴于庆德宫之崇政殿。惟我 王世子率百官行九觞之礼。甚盛举也。于时也。云日清穆。礼乐咸备。 天颜愉悦。众僚醉饱。雍雍熙熙。庶几彷佛于周镐之盛。而吾侪三人。俱以秉笔与焉。可谓荣矣。礼讫。二君以举之盛也。不可以无识也。而谋所以图记为屏。俾不佞以文之。昔欧阳公之居翰苑也。序其内制集。盛言其职事之荣贵。而又自誇其当致治之盛而述作之无不载。至欲归诧于野老田父。今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0H 页
 吾侪之于欧公。虽无能为役。而幸际明时。职忝掌史。当国家有庆之日。而免周南留滞之叹。握彤管而书稀有之举。此诚 君臣之盛际。儒生之至荣。未知欧公所载。亦能有此否乎。而于以归诧于野老田父也。不亦有馀乎。屏凡八幅。其录弁文与名爵者为二幅。为画者六幅。自献酬仪节之繁。尊罍歌乐之盛而皆备焉。他日展玩。庶可指点而想道其盛事云。庚寅九月日序。
吾侪之于欧公。虽无能为役。而幸际明时。职忝掌史。当国家有庆之日。而免周南留滞之叹。握彤管而书稀有之举。此诚 君臣之盛际。儒生之至荣。未知欧公所载。亦能有此否乎。而于以归诧于野老田父也。不亦有馀乎。屏凡八幅。其录弁文与名爵者为二幅。为画者六幅。自献酬仪节之繁。尊罍歌乐之盛而皆备焉。他日展玩。庶可指点而想道其盛事云。庚寅九月日序。送宋翰林圣集晒史五台序
晒史清福也。而人有遇不遇之缘焉。夫抽金匮石室之藏而骋奇诡诙谲之观。以之网罗旧闻。寤寐仙灵者。必以有缘而能焉。前辈之入翰苑者。远则十年。近则三五年。而有不得一至者。观于所谓石室题名录者而可见也。故仕而不至翰林则不能。仕而至翰林而不能以久则不能。能此数者而不幸善病。畏道途鞍马之勤则不能焉。盖以无缘而不能者。有此三者焉。余之居翰苑首尾五年。方其新入也。为右位者六人。昼则裹帽伺候。为没头拜。夜则被其催迫。就灯下。作蝇头细字书。令人欲一吐气不可得。而二右位者方且分路承纶驰驲。纵咏于岭海之间矣。以此视彼。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0L 页
 劳逸奚啻天渊。然当此之时。朝夕所切祝者。惟在于早免椁房之苦况而已。不敢以右位清福自期也。及诸右位之去。余忝为右而继有太白赤裳两行。则余始大偿其宿愿而似近于所谓有缘者焉。然仕而至翰林。非余宜有。而其能不失职以久者亦幸耳。至若疾病之难强。又在二者之外。而前后往返。不以为疲焉若余者。盖直是强作缘者耳。独记其出而游山。则庵僧持杖。官妓挟书。泉洁而沃喉。果红而随匊。而吾不欲归也。及其夜归读史。则治表乱證。杂陈于前。一得一失。互见于后。孤灯照我叹欷。风钟发我警省。而不觉夜之将落矣。当此之时。圣集之视余为不敢望。当与余之视二右位同也。然其仕而至翰林且久者。皆圣集所宜有。而圣集又不如余善病。则乃真有缘者。此则又当为我羡也。且是役也。余之在翰苑也。盖已卜其日矣。圣集日请自往。而余固靳而不许。今余之去翰苑。而圣集始得之矣。岂玆山之缘。于圣集特深。而余固不可复强耶。然余近懒不能作诗。虽见五台月精之胜。无以略写其彷佛。而圣集之诗。方水涌而山出矣。以此应接。必不使山灵落莫。而及归借观。尚足代卧游。不复以不得杖屦其间为叹也。姑书此
劳逸奚啻天渊。然当此之时。朝夕所切祝者。惟在于早免椁房之苦况而已。不敢以右位清福自期也。及诸右位之去。余忝为右而继有太白赤裳两行。则余始大偿其宿愿而似近于所谓有缘者焉。然仕而至翰林。非余宜有。而其能不失职以久者亦幸耳。至若疾病之难强。又在二者之外。而前后往返。不以为疲焉若余者。盖直是强作缘者耳。独记其出而游山。则庵僧持杖。官妓挟书。泉洁而沃喉。果红而随匊。而吾不欲归也。及其夜归读史。则治表乱證。杂陈于前。一得一失。互见于后。孤灯照我叹欷。风钟发我警省。而不觉夜之将落矣。当此之时。圣集之视余为不敢望。当与余之视二右位同也。然其仕而至翰林且久者。皆圣集所宜有。而圣集又不如余善病。则乃真有缘者。此则又当为我羡也。且是役也。余之在翰苑也。盖已卜其日矣。圣集日请自往。而余固靳而不许。今余之去翰苑。而圣集始得之矣。岂玆山之缘。于圣集特深。而余固不可复强耶。然余近懒不能作诗。虽见五台月精之胜。无以略写其彷佛。而圣集之诗。方水涌而山出矣。以此应接。必不使山灵落莫。而及归借观。尚足代卧游。不复以不得杖屦其间为叹也。姑书此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1H 页
 以赠之。
以赠之。文趣序
日余过宿李圣源书室。案有一书曰文趣者。乃农岩先生所尝选以授圣源者。其为书也六编。而文凡二百馀首。起自仲长统乐志论。以及于宋 明诸作。凡文之语涉趣事而见于序记书牍题识之流者。悉收焉。或片言只字之间而爽逾嚼雪。或閒辞漫兴之寓而味深啖蔗。支枕徐读。亹亹忘倦。圣源以余之喜是书也。而令余题其首。余谓为人之趣无过于閒。而为文之趣莫深于淡。閒能发人之趣。淡能生文之趣。今以与是选者观之。皆其人高古閒淡。遗外声利。好自放于泓净峥嵘之会。而与樵牧仙释接。故其言之有趣而可好者如此。而其知而好之也。亦惟其人而已。故唯如圣源之无累能閒者。可以知味此书而亦可以有此书也。农岩之所以遗圣源者。其必有以矣。圣源好为诗。又好为游。其游则是书也未尝不与筇藜漉囊俱。或临水一曲。跻山一级。倦则藉叶席草而息。手是书而讽之。每觉神情散朗。悠然自适。昔人为好游山者而有山足山仆之号。圣源于是有山书矣。
东国自警编序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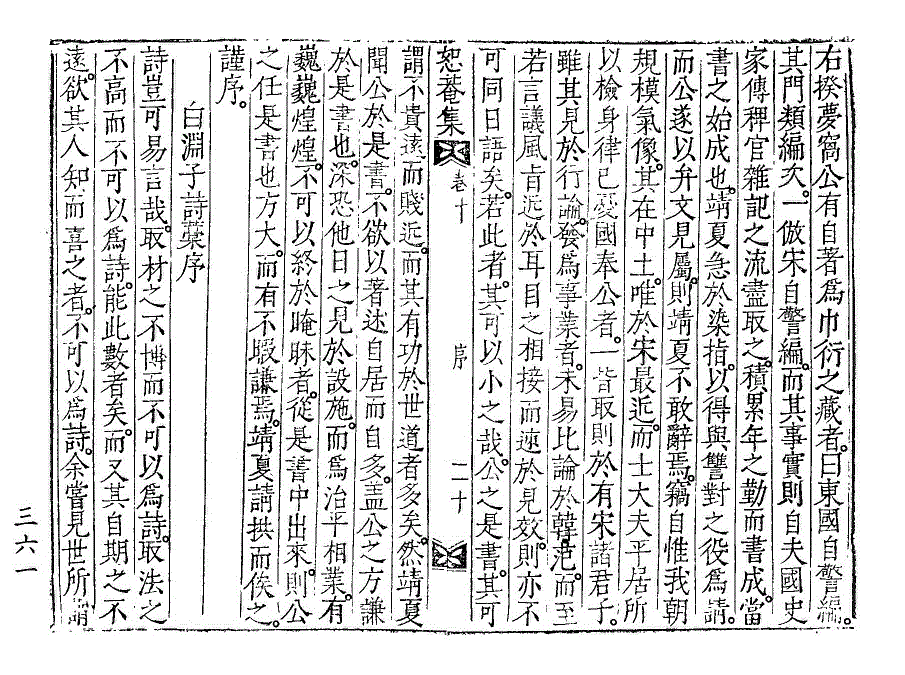 右揆梦窝公有自著为巾衍之藏者。曰东国自警编。其门类编次。一仿宋自警编。而其事实则自夫国史家传稗官杂记之流尽取之。积累年之勤而书成。当书之始成也。靖夏急于染指。以得与雠对之役为请。而公遂以弁文见属。则靖夏不敢辞焉。窃自惟我朝规模气像。其在中土。唯于宋最近。而士大夫平居所以检身律己忧国奉公者。一皆取则于有宋诸君子。虽其见于行论。发为事业者。未易比论于韩,范。而至若言议风旨近于耳目之相接而速于见效。则亦不可同日语矣。若此者。其可以小之哉。公之是书。其可谓不贵远而贱近。而其有功于世道者多矣。然靖夏闻公于是书。不欲以著述自居而自多。盖公之方谦于是书也。深恐他日之见于设施。而为治平相业。有巍巍煌煌。不可以终于晻昧者。从是书中出来。则公之任是书也方大。而有不暇谦焉。靖夏请拱而俟之。谨序。
右揆梦窝公有自著为巾衍之藏者。曰东国自警编。其门类编次。一仿宋自警编。而其事实则自夫国史家传稗官杂记之流尽取之。积累年之勤而书成。当书之始成也。靖夏急于染指。以得与雠对之役为请。而公遂以弁文见属。则靖夏不敢辞焉。窃自惟我朝规模气像。其在中土。唯于宋最近。而士大夫平居所以检身律己忧国奉公者。一皆取则于有宋诸君子。虽其见于行论。发为事业者。未易比论于韩,范。而至若言议风旨近于耳目之相接而速于见效。则亦不可同日语矣。若此者。其可以小之哉。公之是书。其可谓不贵远而贱近。而其有功于世道者多矣。然靖夏闻公于是书。不欲以著述自居而自多。盖公之方谦于是书也。深恐他日之见于设施。而为治平相业。有巍巍煌煌。不可以终于晻昧者。从是书中出来。则公之任是书也方大。而有不暇谦焉。靖夏请拱而俟之。谨序。白渊子诗藁序
诗岂可易言哉。取材之不博而不可以为诗。取法之不高而不可以为诗。能此数者矣。而又其自期之不远。欲其人知而喜之者。不可以为诗。余尝见世所谓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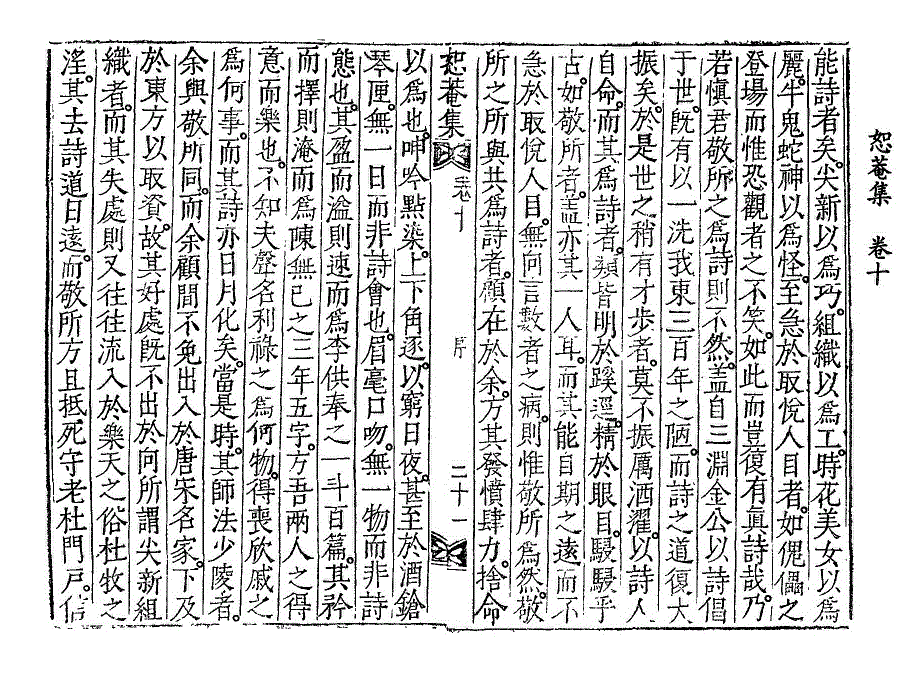 能诗者矣。尖新以为巧。组织以为工。时花美女以为丽。牛鬼蛇神以为怪。至急于取悦人目者。如傀儡之登场而惟恐观者之不笑。如此而岂复有真诗哉。乃若慎君敬所之为诗则不然。盖自三渊金公以诗倡于世。既有以一洗我东三百年之陋。而诗之道复大振矣。于是世之稍有才步者。莫不振厉洒濯。以诗人自命。而其为诗者。类皆明于蹊径。精于眼目。骎骎乎古。如敬所者。盖亦其一人耳。而其能自期之远而不急于取悦人目。无向言数者之病。则惟敬所为然。敬所之所与共为诗者。顾在于余。方其发愤肆力。舍命以为也。呻吟点染。上下角逐。以穷日夜。甚至于酒鎗琴匣。无一日而非诗会也。眉毫口吻。无一物而非诗态也。其盈而溢则速而为李供奉之一斗百篇。其矜而择则淹而为陈无己之三年五字。方吾两人之得意而乐也。不知夫声名利禄之为何物。得丧欣戚之为何事。而其诗亦日月化矣。当是时。其师法少陵者。余与敬所同。而余顾间不免出入于唐宋名家。下及于东方以取资。故其好处既不出于向所谓尖新组织者。而其失处则又往往流入于乐天之俗杜牧之淫。其去诗道日远。而敬所方且抵死守老杜门户。信
能诗者矣。尖新以为巧。组织以为工。时花美女以为丽。牛鬼蛇神以为怪。至急于取悦人目者。如傀儡之登场而惟恐观者之不笑。如此而岂复有真诗哉。乃若慎君敬所之为诗则不然。盖自三渊金公以诗倡于世。既有以一洗我东三百年之陋。而诗之道复大振矣。于是世之稍有才步者。莫不振厉洒濯。以诗人自命。而其为诗者。类皆明于蹊径。精于眼目。骎骎乎古。如敬所者。盖亦其一人耳。而其能自期之远而不急于取悦人目。无向言数者之病。则惟敬所为然。敬所之所与共为诗者。顾在于余。方其发愤肆力。舍命以为也。呻吟点染。上下角逐。以穷日夜。甚至于酒鎗琴匣。无一日而非诗会也。眉毫口吻。无一物而非诗态也。其盈而溢则速而为李供奉之一斗百篇。其矜而择则淹而为陈无己之三年五字。方吾两人之得意而乐也。不知夫声名利禄之为何物。得丧欣戚之为何事。而其诗亦日月化矣。当是时。其师法少陵者。余与敬所同。而余顾间不免出入于唐宋名家。下及于东方以取资。故其好处既不出于向所谓尖新组织者。而其失处则又往往流入于乐天之俗杜牧之淫。其去诗道日远。而敬所方且抵死守老杜门户。信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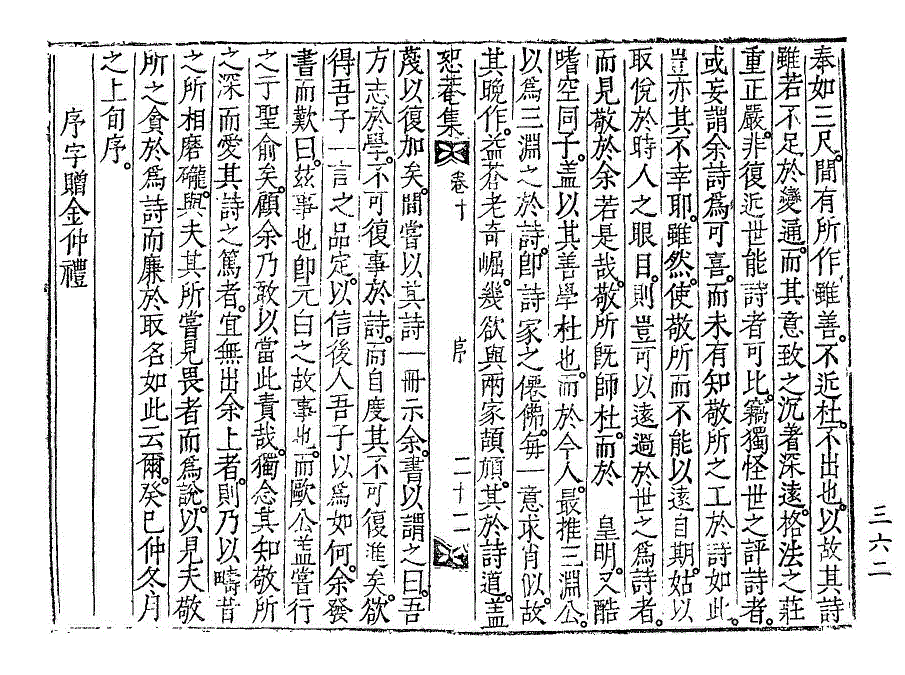 奉如三尺。间有所作。虽善。不近杜。不出也。以故其诗虽若不足于变通。而其意致之沉着深远。格法之庄重正严。非复近世能诗者可比。窃独怪世之评诗者。或妄谓余诗为可喜。而未有知敬所之工于诗如此。岂亦其不幸耶。虽然。使敬所而不能以远自期。姑以取悦于时人之眼目。则岂可以远过于世之为诗者。而见敬于余若是哉。敬所既师杜。而于 皇明。又酷嗜空同子。盖以其善学杜也。而于今人。最推三渊公。以为三渊之于诗。即诗家之仙佛。每一意求肖似。故其晚作。益苍老奇崛。几欲与两家颉颃。其于诗道。盖蔑以复加矣。间尝以其诗一册示余。书以谓之曰。吾方志于学。不可复事于诗。而自度其不可复进矣。欲得吾子一言之品定。以信后人吾子以为如何。余发书而叹曰。玆事也即元白之故事也。而欧公盖尝行之于圣俞矣。顾余乃敢以当此责哉。独念其知敬所之深而爱其诗之笃者。宜无出余上者。则乃以畴昔之所相磨砻。与夫其所尝见畏者而为说。以见夫敬所之贪于为诗而廉于取名如此云尔。癸巳仲冬月之上旬序。
奉如三尺。间有所作。虽善。不近杜。不出也。以故其诗虽若不足于变通。而其意致之沉着深远。格法之庄重正严。非复近世能诗者可比。窃独怪世之评诗者。或妄谓余诗为可喜。而未有知敬所之工于诗如此。岂亦其不幸耶。虽然。使敬所而不能以远自期。姑以取悦于时人之眼目。则岂可以远过于世之为诗者。而见敬于余若是哉。敬所既师杜。而于 皇明。又酷嗜空同子。盖以其善学杜也。而于今人。最推三渊公。以为三渊之于诗。即诗家之仙佛。每一意求肖似。故其晚作。益苍老奇崛。几欲与两家颉颃。其于诗道。盖蔑以复加矣。间尝以其诗一册示余。书以谓之曰。吾方志于学。不可复事于诗。而自度其不可复进矣。欲得吾子一言之品定。以信后人吾子以为如何。余发书而叹曰。玆事也即元白之故事也。而欧公盖尝行之于圣俞矣。顾余乃敢以当此责哉。独念其知敬所之深而爱其诗之笃者。宜无出余上者。则乃以畴昔之所相磨砻。与夫其所尝见畏者而为说。以见夫敬所之贪于为诗而廉于取名如此云尔。癸巳仲冬月之上旬序。序字赠金仲礼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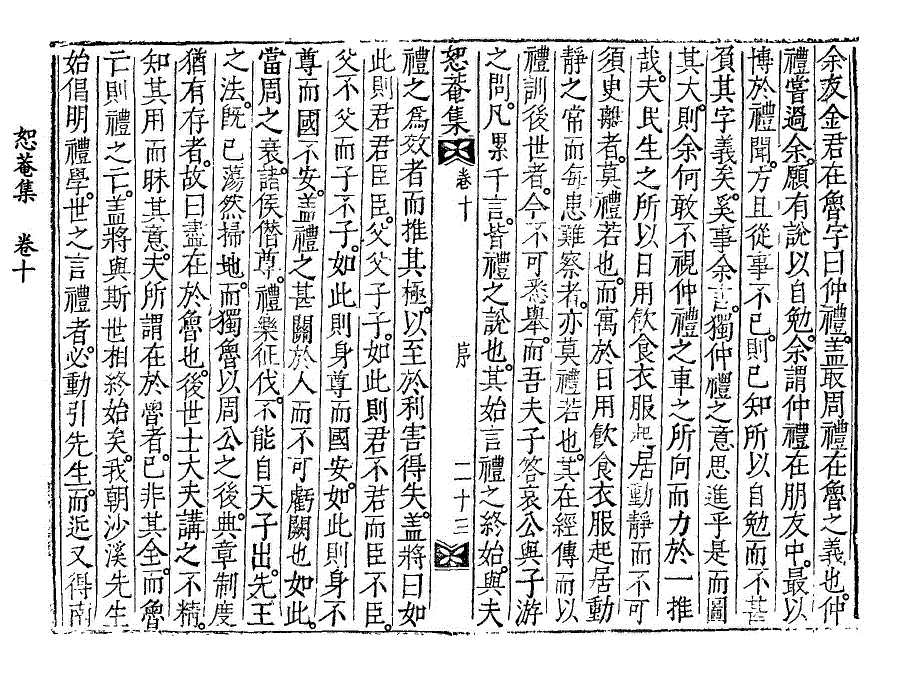 余友金君在鲁字曰仲礼。盖取周礼在鲁之义也。仲礼尝过余。愿有说以自勉。余谓仲礼在朋友中。最以博于礼闻。方且从事不已。则已知所以自勉而不甚负其字义矣。奚事余言。独仲礼之意思进乎是而图其大。则余何敢不视仲礼之车之所向而力于一推哉。夫民生之所以日用饮食衣服起居动静而不可须臾离者。莫礼若也。而寓于日用饮食衣服起居动静之常而每患难察者。亦莫礼若也。其在经传而以礼训后世者。今不可悉举。而吾夫子答哀公与子游之问。凡累千言。皆礼之说也。其始言礼之终始。与夫礼之为效者而推其极。以至于利害得失。盖将曰如此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则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如此则身尊而国安。如此则身不尊而国不安。盖礼之甚关于人而不可亏阙也如此。当周之衰。诸侯僭尊。礼乐征伐。不能自天子出。先王之法。既已荡然扫地。而独鲁以周公之后。典章制度犹有存者。故曰尽在于鲁也。后世士大夫讲之不精。知其用而昧其意。夫所谓在于鲁者。已非其全。而鲁亡则礼之亡。盖将与斯世相终始矣。我朝沙溪先生始倡明礼学。世之言礼者。必动引先生。而近又得南
余友金君在鲁字曰仲礼。盖取周礼在鲁之义也。仲礼尝过余。愿有说以自勉。余谓仲礼在朋友中。最以博于礼闻。方且从事不已。则已知所以自勉而不甚负其字义矣。奚事余言。独仲礼之意思进乎是而图其大。则余何敢不视仲礼之车之所向而力于一推哉。夫民生之所以日用饮食衣服起居动静而不可须臾离者。莫礼若也。而寓于日用饮食衣服起居动静之常而每患难察者。亦莫礼若也。其在经传而以礼训后世者。今不可悉举。而吾夫子答哀公与子游之问。凡累千言。皆礼之说也。其始言礼之终始。与夫礼之为效者而推其极。以至于利害得失。盖将曰如此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则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如此则身尊而国安。如此则身不尊而国不安。盖礼之甚关于人而不可亏阙也如此。当周之衰。诸侯僭尊。礼乐征伐。不能自天子出。先王之法。既已荡然扫地。而独鲁以周公之后。典章制度犹有存者。故曰尽在于鲁也。后世士大夫讲之不精。知其用而昧其意。夫所谓在于鲁者。已非其全。而鲁亡则礼之亡。盖将与斯世相终始矣。我朝沙溪先生始倡明礼学。世之言礼者。必动引先生。而近又得南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3L 页
 溪先生而发挥之然后。世几知礼之所向矣。然士之治礼者尚少。今仲礼之名与字也。盖将视礼为己事矣。夫以天下之大。而在于一小鲁。则鲁为荣而礼之存者微矣。以天下之大。而在于一仲礼。则仲礼愈荣而礼之存者愈微矣。仲礼于此。顾安得不勉也。故其沉潜累年而爬栉疏瀹。殆无遗焉。凡吾辈之有聚讼者。惟仲礼焉是归。而仲礼之应之也。如富者之不穷于用财。亦尝一游大学。疏斥当路之乱礼者。虽以此得罪于时。而有识君子至今韪之。呜呼。此殆近乎求诸野矣。今仲礼既已致身荣途。其闻日达。意其将朝暮鶱腾。历金门而上玉堂矣。使仲礼而益勉乎。则凡邦礼之所疑阙而不举者。举将待仲礼而询焉。然则向所谓求诸野者。将见求诸朝矣。仲礼其可不思有以益勉乎。然此在仲礼。犹为小者尔。顾今夷羯秽华。四海腥膻。变礼乐声明之区而为毁冠裂冕之俗。独我箕域有东鲁之望。有王者作而欲兴三代之礼乐者。其不以我东为小。仲礼为微而来取也明矣。未知仲礼其亦思所以应之者乎。余谓仲礼之于大者。有不可不勉者如此。夫然后始可以毋负其字义。而仲礼之事乃毕矣。此岂非仲礼之所欲卒闻于余者乎。
溪先生而发挥之然后。世几知礼之所向矣。然士之治礼者尚少。今仲礼之名与字也。盖将视礼为己事矣。夫以天下之大。而在于一小鲁。则鲁为荣而礼之存者微矣。以天下之大。而在于一仲礼。则仲礼愈荣而礼之存者愈微矣。仲礼于此。顾安得不勉也。故其沉潜累年而爬栉疏瀹。殆无遗焉。凡吾辈之有聚讼者。惟仲礼焉是归。而仲礼之应之也。如富者之不穷于用财。亦尝一游大学。疏斥当路之乱礼者。虽以此得罪于时。而有识君子至今韪之。呜呼。此殆近乎求诸野矣。今仲礼既已致身荣途。其闻日达。意其将朝暮鶱腾。历金门而上玉堂矣。使仲礼而益勉乎。则凡邦礼之所疑阙而不举者。举将待仲礼而询焉。然则向所谓求诸野者。将见求诸朝矣。仲礼其可不思有以益勉乎。然此在仲礼。犹为小者尔。顾今夷羯秽华。四海腥膻。变礼乐声明之区而为毁冠裂冕之俗。独我箕域有东鲁之望。有王者作而欲兴三代之礼乐者。其不以我东为小。仲礼为微而来取也明矣。未知仲礼其亦思所以应之者乎。余谓仲礼之于大者。有不可不勉者如此。夫然后始可以毋负其字义。而仲礼之事乃毕矣。此岂非仲礼之所欲卒闻于余者乎。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4H 页
 呜呼。仲礼其厚自树哉。
呜呼。仲礼其厚自树哉。桃源图屏诗小引
画家铺叙。莫难于桃源。盖欲尽事景。则失于凡浅。欲取意态。则嫌其没失。以故古绘素家罕有下手者。近有孟永光者。善为阴画。尝作此图。于松林杳冥中。藏一溪宛转。着渔子于林外。若窥寻者。而远有花气迷人。自以为绝笔。今为余家物。然此乃只得其意者。犹未尽夫事景。今者从人借得仇十洲英所制本。其铺叙自渊明诗以下尽取之。用笔工致。意景俱足爱玩。不能释手。乃命院史李𤦮。摸取为屏。计工为五十日。其精得十之七八。遂为传家宝藏。仍取古人诸歌行题屏背。盖写桃源者。至十洲而极其妙。歌桃源者。至五峰而极其变。而慕桃源者。至余而极其想。三者不可以无识。遂成四绝。书其后。亦以自笑其妄而为多事之戒云。
离别一首赠同学某生
古人之道离别旧矣。自苏李河梁之作。以及魏晋氏诸人。如谢公作恶之语。隐侯相思之句。皆出于握手写情。临歧赠言。丁宁反覆。恻怆动人。千载之下。读者代伤焉。夫冠之弊而尝加乎吾首也。履之毁而尝纳
恕庵集卷之十 第 364L 页
 乎吾足也。则人于二物也。未始无情也。况斯人之好我者。接膝而共业。交臂而并游。死生契阔。相视莫逆者。今乃一朝割然告别。重之以山河之间阔。鳞羽之难凭。则宜其行与居者。两难为情矣。然此亦蔽于近而不达理之过也。夫士之有志者。孰不愿生于唐虞三代之世。获睹夫雍熙之治礼乐之风而以洗其耳目也。亦孰不愿亲炙于尧舜周公孔孟之圣人以叩其所疑也哉。今吾于世。既已后唐虞三代矣。于人。既已失尧舜周公孔孟矣。生之有先后而时之限古今。则余虽恨焉而顾未敢以为恨也。夫聚之不能无散。犹后之不能齐先也。近而为聚散。远而为先后。今吾知先后之不可齐而不知聚散之不可常。岂达论也哉。今自无穷者而言也。则彼千岁之违我者。举将为别也。别其可既乎。就其简者而言也。则虽吾与彼之无辨也。岂复有离别乎。有某生某者。从余游既有年矣。今其归也。有若恋恋不能舍者。故临别。余告之以此。呜呼。读吾说者。可以知离别之无穷矣。亦可无离别之悲矣。
乎吾足也。则人于二物也。未始无情也。况斯人之好我者。接膝而共业。交臂而并游。死生契阔。相视莫逆者。今乃一朝割然告别。重之以山河之间阔。鳞羽之难凭。则宜其行与居者。两难为情矣。然此亦蔽于近而不达理之过也。夫士之有志者。孰不愿生于唐虞三代之世。获睹夫雍熙之治礼乐之风而以洗其耳目也。亦孰不愿亲炙于尧舜周公孔孟之圣人以叩其所疑也哉。今吾于世。既已后唐虞三代矣。于人。既已失尧舜周公孔孟矣。生之有先后而时之限古今。则余虽恨焉而顾未敢以为恨也。夫聚之不能无散。犹后之不能齐先也。近而为聚散。远而为先后。今吾知先后之不可齐而不知聚散之不可常。岂达论也哉。今自无穷者而言也。则彼千岁之违我者。举将为别也。别其可既乎。就其简者而言也。则虽吾与彼之无辨也。岂复有离别乎。有某生某者。从余游既有年矣。今其归也。有若恋恋不能舍者。故临别。余告之以此。呜呼。读吾说者。可以知离别之无穷矣。亦可无离别之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