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恕庵集卷之六 第 x 页
恕庵集卷之六(平山申靖夏正甫 著)
书
书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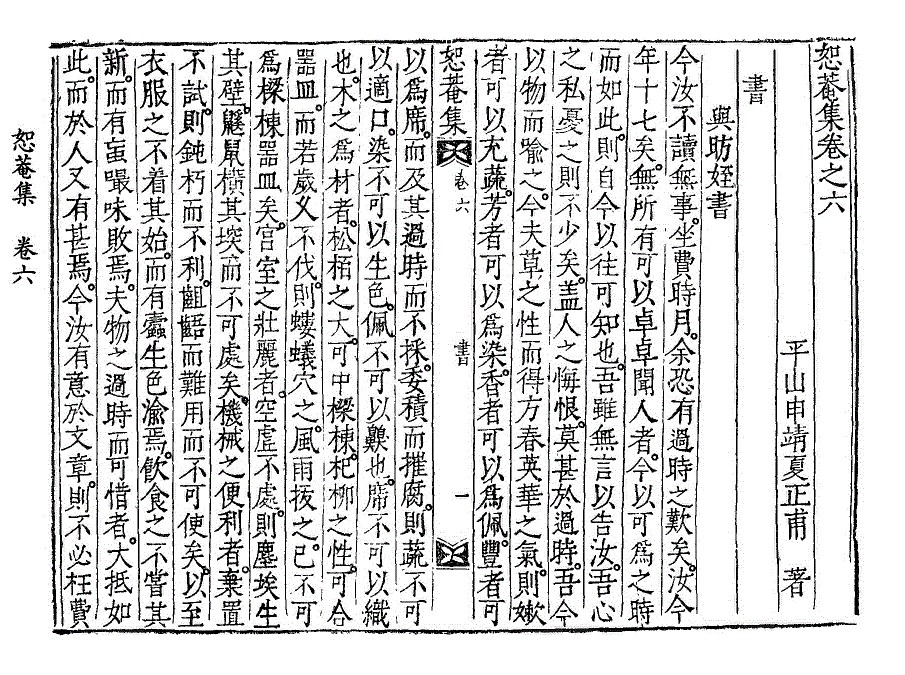 与昉侄书
与昉侄书今汝不读无事。坐费时月。余恐有过时之叹矣。汝今年十七矣。无所有可以卓卓闻人者。今以可为之时而如此。则自今以往可知也。吾虽无言以告汝。吾心之私忧之则不少矣。盖人之悔恨。莫甚于过时。吾今以物而喻之。今夫草之性而得方春英华之气。则嫩者可以充蔬。芳者可以为染。香者可以为佩。丰者可以为席。而及其过时而不采。委积而摧腐。则蔬不可以适口。染不可以生色。佩不可以嗅也。席不可以织也。木之为材者。松柏之大。可中梁栋。杞柳之性。可合器皿。而若岁久不伐。则蝼蚁穴之。风雨拔之。已不可为梁栋器皿矣。宫室之壮丽者。空虚不处。则尘埃生其壁。鼷鼠横其突而不可处矣。机械之便利者。弃置不试。则钝朽而不利。龃龉而难用而不可使矣。以至衣服之不着其始。而有蠹生色渝焉。饮食之不尝其新。而有虻嘬味败焉。夫物之过时而可惜者。大抵如此。而于人又有甚焉。今汝有意于文章。则不必枉费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79L 页
 言语。亦不必过用思量。目下便可下工。不此之为。而今且犹豫迁就。坐耗光阴。余恐于是乎失其时而终不能以有为矣。凡读书作文。必专于年少时。盖唯年少者。能无物欲世故。为文而去此二者。何所不至哉。及至年大。一涉世故。则较计之智。忧患之念。得丧之虑。应接之众。出入之烦。纷纭而至。缠绕而来。更无把笔为文之日矣。于是时虽咄咄追悔。更欲求一日少年。岂可得也。余十五岁。始知为文之可贵。又其所见如此。故唯以欧阳公多读多作两句语为师。昼读夜诵。未尝暂辍。若秋尽而冬生。则其意汲汲然如夏农之治田。其甚者。诵读之声。常发于梦寐。又其制作时。则笔砚未尝离座。出入辄以自随。如此者五年而后有得。自昨年已复厌作。此乃吾所亲见者。今汝年方在余看读不离口。制作不离手之年。而犹如此。计其所读。不过吾半。所作尤绝少。无我之勤而欲有我之所有。岂不大惑欤。然独所恃于汝者。唯其才与识耳。汝之所事既如此。而时作一二篇。亦有可喜者。至于古人议论。以余之终日反覆难通者。而或得汝一言而开悟。有如此才识。而犹且不勤笃以过时而无成。则岂不为可恨之甚者乎。有其才而不为。不如无其
言语。亦不必过用思量。目下便可下工。不此之为。而今且犹豫迁就。坐耗光阴。余恐于是乎失其时而终不能以有为矣。凡读书作文。必专于年少时。盖唯年少者。能无物欲世故。为文而去此二者。何所不至哉。及至年大。一涉世故。则较计之智。忧患之念。得丧之虑。应接之众。出入之烦。纷纭而至。缠绕而来。更无把笔为文之日矣。于是时虽咄咄追悔。更欲求一日少年。岂可得也。余十五岁。始知为文之可贵。又其所见如此。故唯以欧阳公多读多作两句语为师。昼读夜诵。未尝暂辍。若秋尽而冬生。则其意汲汲然如夏农之治田。其甚者。诵读之声。常发于梦寐。又其制作时。则笔砚未尝离座。出入辄以自随。如此者五年而后有得。自昨年已复厌作。此乃吾所亲见者。今汝年方在余看读不离口。制作不离手之年。而犹如此。计其所读。不过吾半。所作尤绝少。无我之勤而欲有我之所有。岂不大惑欤。然独所恃于汝者。唯其才与识耳。汝之所事既如此。而时作一二篇。亦有可喜者。至于古人议论。以余之终日反覆难通者。而或得汝一言而开悟。有如此才识。而犹且不勤笃以过时而无成。则岂不为可恨之甚者乎。有其才而不为。不如无其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0H 页
 才而不为也。今汝于物。若见过时而不用。如向吾所言者。则其心必为之恻然感念。悯然叹惜。此固仁人之用心也。至于身而不思所以可惜者何哉。古之过时而能文者。宋之苏明允。唐之高达夫。有此二子在焉耳。今汝取此二子为證。则差可慰心。而但如此才。世未尝多有。今欲以衰末有限之才。学古人绝伦之事。岂不大惑且谬也。而抑二子早自觉悟。则又安知其所得之止此也。且向也闻汝言。乃曰文章者不可力求。不可造次而得。其自知如此。故虽平居作文时。未尝容易下笔。或有作不甚奇。则随以裂去。其视今世为文之士。未尝略窥古人之藩篱。而妄谓与古人同者则有间矣。是不为妄则幸矣。而然有不免其弊者。吾当告汝。夫为文章者。又不可不先立其志气。不立其志气。则鲜有不为颓堕自沮而不振矣。余于始者读尚书禹贡篇。见其笔势之雄高。以为为文者当如此。既见马史。又一以太史公自期。则比向者见禹贡时。其气少降矣。及嗜好于唐宋八君子之文。知 皇明诸大家虚自壮耀之习然后。又以为不可强作心意。务张形势。反致无实。则复笑向日自期之妄僭。见其所作之出于十五岁以上者。辄觉赧然发愧。投
才而不为也。今汝于物。若见过时而不用。如向吾所言者。则其心必为之恻然感念。悯然叹惜。此固仁人之用心也。至于身而不思所以可惜者何哉。古之过时而能文者。宋之苏明允。唐之高达夫。有此二子在焉耳。今汝取此二子为證。则差可慰心。而但如此才。世未尝多有。今欲以衰末有限之才。学古人绝伦之事。岂不大惑且谬也。而抑二子早自觉悟。则又安知其所得之止此也。且向也闻汝言。乃曰文章者不可力求。不可造次而得。其自知如此。故虽平居作文时。未尝容易下笔。或有作不甚奇。则随以裂去。其视今世为文之士。未尝略窥古人之藩篱。而妄谓与古人同者则有间矣。是不为妄则幸矣。而然有不免其弊者。吾当告汝。夫为文章者。又不可不先立其志气。不立其志气。则鲜有不为颓堕自沮而不振矣。余于始者读尚书禹贡篇。见其笔势之雄高。以为为文者当如此。既见马史。又一以太史公自期。则比向者见禹贡时。其气少降矣。及嗜好于唐宋八君子之文。知 皇明诸大家虚自壮耀之习然后。又以为不可强作心意。务张形势。反致无实。则复笑向日自期之妄僭。见其所作之出于十五岁以上者。辄觉赧然发愧。投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0L 页
 之于火。然使我终始于此。以有今日。而回视赧然笑昔之所为者。乃妄与僭之力也。故曰为文章者。不可不早立其志气。今汝之心。有今我之惰。而今汝之业。无旧我之勤。又太半为疾病所夺。若果因循无成。而终为自弃之归。则岂不大可恨乎。急宜先取史汉中一书。读三二十遍然后。复易他书。务领略其要。亦须屏绝他念。于制作时。一以古人为师。不以其难而自沮。不以其苦而或怠。则高才刚力。自有可得。庶无过时之叹矣。此余之所以区区有望于汝也。吾之所欲告汝者久矣。而尚有未暇者。朝作跋文。偶因举笔而及之。一一细看。用以自警至可。
之于火。然使我终始于此。以有今日。而回视赧然笑昔之所为者。乃妄与僭之力也。故曰为文章者。不可不早立其志气。今汝之心。有今我之惰。而今汝之业。无旧我之勤。又太半为疾病所夺。若果因循无成。而终为自弃之归。则岂不大可恨乎。急宜先取史汉中一书。读三二十遍然后。复易他书。务领略其要。亦须屏绝他念。于制作时。一以古人为师。不以其难而自沮。不以其苦而或怠。则高才刚力。自有可得。庶无过时之叹矣。此余之所以区区有望于汝也。吾之所欲告汝者久矣。而尚有未暇者。朝作跋文。偶因举笔而及之。一一细看。用以自警至可。上农岩先生书
靖夏齿少学浅。所见闻孤陋。区区之愿。窃欲得奉教于搢绅先生者。非一日积矣。窃见执事厚德高风。耸动一世。道学文章。度越前辈。其立朝也。未尽其有。而其山林也。讲求涵养。有以自乐。出处进退。真古所谓名世之贤者。凡此数者。皆今世之士所共谈。而尤靖夏之所向慕而叹其不得见者也。于斯时也。思之甚则昼诵其文。掩其卷则夜梦其人。靖夏之所以慕执事者。其志可谓苦矣。其诚非不切矣。而顾自以为才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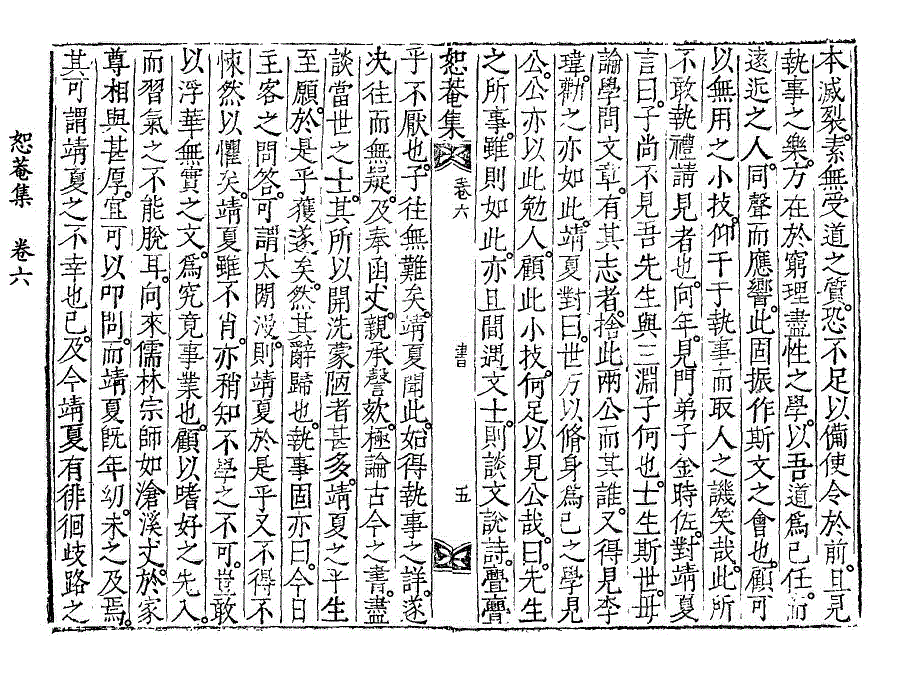 本灭裂。素无受道之质。恐不足以备使令于前。且见执事之乐。方在于穷理尽性之学。以吾道为己任。而远近之人。同声而应响。此固振作斯文之会也。顾可以无用之小技。仰干于执事而取人之讥笑哉。此所不敢执礼请见者也。向年。见门弟子金时佐。对靖夏言曰。子尚不见吾先生与三渊子何也。士生斯世。毋论学问文章。有其志者。舍此两公而其谁。又得见李玮。劝之亦如此。靖夏对曰。世方以脩身为己之学见公。公亦以此勉人。顾此小技。何足以见公哉。曰。先生之所事。虽则如此。亦且间遇文士。则谈文说诗。亹亹乎不厌也。子往无难矣。靖夏闻此。始得执事之详。遂决往而无疑。及奉函丈。亲承謦欬。极论古今之书。尽谈当世之士。其所以开洗蒙陋者甚多。靖夏之平生至愿。于是乎获遂矣。然其辞归也。执事固亦曰。今日主客之问答。可谓太閒漫。则靖夏于是乎又不得不悚然以惧矣。靖夏虽不肖。亦稍知不学之不可。岂敢以浮华无实之文。为究竟事业也。顾以嗜好之先入。而习气之不能脱耳。向来儒林宗师如沧溪丈。于家尊相与甚厚。宜可以叩问。而靖夏既年幼。未之及焉。其可谓靖夏之不幸也已。及今靖夏有徘徊歧路之
本灭裂。素无受道之质。恐不足以备使令于前。且见执事之乐。方在于穷理尽性之学。以吾道为己任。而远近之人。同声而应响。此固振作斯文之会也。顾可以无用之小技。仰干于执事而取人之讥笑哉。此所不敢执礼请见者也。向年。见门弟子金时佐。对靖夏言曰。子尚不见吾先生与三渊子何也。士生斯世。毋论学问文章。有其志者。舍此两公而其谁。又得见李玮。劝之亦如此。靖夏对曰。世方以脩身为己之学见公。公亦以此勉人。顾此小技。何足以见公哉。曰。先生之所事。虽则如此。亦且间遇文士。则谈文说诗。亹亹乎不厌也。子往无难矣。靖夏闻此。始得执事之详。遂决往而无疑。及奉函丈。亲承謦欬。极论古今之书。尽谈当世之士。其所以开洗蒙陋者甚多。靖夏之平生至愿。于是乎获遂矣。然其辞归也。执事固亦曰。今日主客之问答。可谓太閒漫。则靖夏于是乎又不得不悚然以惧矣。靖夏虽不肖。亦稍知不学之不可。岂敢以浮华无实之文。为究竟事业也。顾以嗜好之先入。而习气之不能脱耳。向来儒林宗师如沧溪丈。于家尊相与甚厚。宜可以叩问。而靖夏既年幼。未之及焉。其可谓靖夏之不幸也已。及今靖夏有徘徊歧路之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1L 页
 叹。而得执事一言之警。开示其门户。靖夏其敢不感激奋励。尽力而向前乎。若蒙执事不以为不可教而收之门下。教育成就。终始其惠。则岂非区区之幸也。辞退之后。忽复改岁。不审履玆新春。体候何如。靖夏顿首再拜。
叹。而得执事一言之警。开示其门户。靖夏其敢不感激奋励。尽力而向前乎。若蒙执事不以为不可教而收之门下。教育成就。终始其惠。则岂非区区之幸也。辞退之后。忽复改岁。不审履玆新春。体候何如。靖夏顿首再拜。上农岩先生书
累日得陪杖屦。心之私幸。有不可言。而忽尔违拜。遂以至今。区区向慕。岂胜仰喻。不审比者阴雨。道体动静若何。适有小欲承禀者。敢以书奉。日者因李玮得闻下诲。以为自宋六君子以后。文章之道。荡然几尽。独能达其堂奥。接其衣钵者。唯陆务观一人云。靖夏于斯时。方嗜好陆诗。复不意其文之亦能至斯。未暇染指矣。昨来偶阅古文诸家选。得观其论序一二篇。其宏肆俊伟之旨。与欧公酷似胜。其诗句远甚。此老平生。独以诗显而未有以文称何也。盖当赵宋之世。文章之道。可谓盛矣。一自欧曾洒濯于前。二苏和唱于后。如张文潜,李方叔,晁无咎,陈无己,黄鲁直,秦少游诸人。蔚然辈出。观其所为文。亦足以不死千古。而独恨其旨不赡博。体未兼备。要不可以追配古作家之盛。至于此老。其力量材具。本非数子之比。而况其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2H 页
 篇什富盛。不如数子之仅见。若使之比肩数子。北面于欧苏。则是大不可。而世之以白苏王数公。谓有诗文之兼美。而独不及于放翁者。恐不足为具眼者论。未知执事以此言为如何也。如闻此书见在案下。果然否。切欲得见其未见者。如或见在。因来便寄下。如已送还本处。亦望指教其可借之路也。区区之诚。辄不自揆。窃欲与李玮,慎无逸辈共相论断。钞成一书。以续八家之后。意虽妄僭。其诚则可见也。若蒙执事恕其妄僭。而亦示其钞选取舍之方。则是又大幸也。未知如何。靖夏本来有火郁之證。自春后转剧。所用药物。尚未见效。无以致身函丈。获承馀论。瞻望门墙。只有怅悬而已。馀怀烦不敢仰尽。
篇什富盛。不如数子之仅见。若使之比肩数子。北面于欧苏。则是大不可。而世之以白苏王数公。谓有诗文之兼美。而独不及于放翁者。恐不足为具眼者论。未知执事以此言为如何也。如闻此书见在案下。果然否。切欲得见其未见者。如或见在。因来便寄下。如已送还本处。亦望指教其可借之路也。区区之诚。辄不自揆。窃欲与李玮,慎无逸辈共相论断。钞成一书。以续八家之后。意虽妄僭。其诚则可见也。若蒙执事恕其妄僭。而亦示其钞选取舍之方。则是又大幸也。未知如何。靖夏本来有火郁之證。自春后转剧。所用药物。尚未见效。无以致身函丈。获承馀论。瞻望门墙。只有怅悬而已。馀怀烦不敢仰尽。与金三渊书
靖夏自幼时。慕长者至甚。如恐不得见。况如执事之问学文章。即其思慕又可知也。靖夏十一二岁。即有意治声诗。虽其所得。无敢望古人。而其所乐。亦足有以忘其苦者。窃自以为东方无诗人。若挹翠轩之神韵。苏斋之骨力。非不卓然奇矣。而翠轩微失于三尺。苏斋太剥其天真。要之俱不得诗家之正道焉。今执事之诗。其好处固如二公。而兼无二公之颇颣。此靖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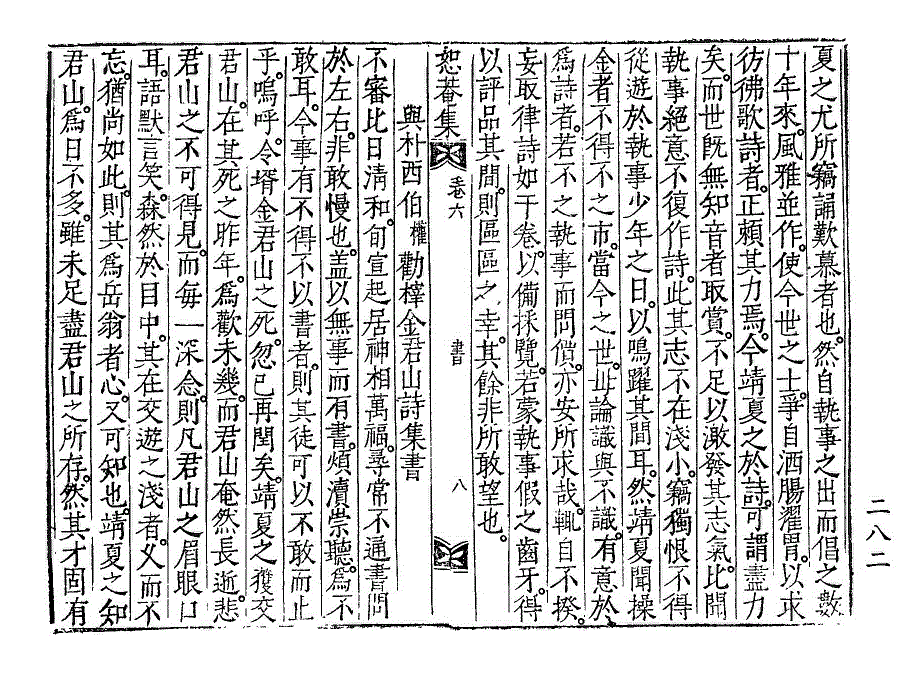 夏之尤所窃诵叹慕者也。然自执事之出而倡之数十年来。风雅并作。使今世之士。争自洒肠濯胃。以求彷佛歌诗者。正赖其力焉。今靖夏之于诗。可谓尽力矣。而世既无知音者取赏。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比闻执事绝意不复作诗。此其志不在浅小。窃独恨不得从游于执事少年之日。以鸣跃其间耳。然靖夏闻操金者不得不之市。当今之世。毋论识与不识。有意于为诗者。若不之执事而问价。亦安所求哉。辄自不揆。妄取律诗如干卷。以备采览。若蒙执事假之齿牙。得以评品其间。则区区之幸。其馀非所敢望也。
夏之尤所窃诵叹慕者也。然自执事之出而倡之数十年来。风雅并作。使今世之士。争自洒肠濯胃。以求彷佛歌诗者。正赖其力焉。今靖夏之于诗。可谓尽力矣。而世既无知音者取赏。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比闻执事绝意不复作诗。此其志不在浅小。窃独恨不得从游于执事少年之日。以鸣跃其间耳。然靖夏闻操金者不得不之市。当今之世。毋论识与不识。有意于为诗者。若不之执事而问价。亦安所求哉。辄自不揆。妄取律诗如干卷。以备采览。若蒙执事假之齿牙。得以评品其间。则区区之幸。其馀非所敢望也。与朴西伯(权)劝梓金君山诗集书
不审比日清和。旬宣起居神相万福。寻常不通书问于左右。非敢慢也。盖以无事而有书。烦渎崇听。为不敢耳。今事有不得不以书者。则其徒可以不敢而止乎。呜呼。令婿金君山之死。忽已再闰矣。靖夏之获交君山。在其死之昨年。为欢未几。而君山奄然长逝。悲君山之不可得见。而每一深念。则凡君山之眉眼口耳。语默言笑。森然于目中。其在交游之浅者。久而不忘。犹尚如此。则其为岳翁者心。又可知也。靖夏之知君山。为日不多。虽未足尽君山之所存。然其才固有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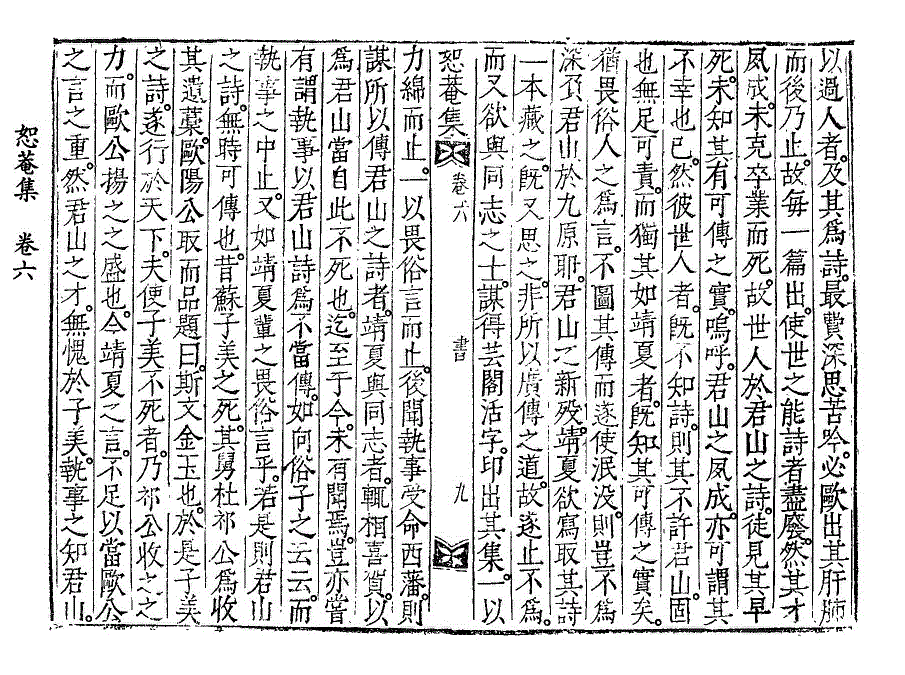 以过人者。及其为诗。最费深思苦吟。必欧出其肝肺而后乃止。故每一篇出。使世之能诗者尽废。然其才夙成。未克卒业而死。故世人于君山之诗。徒见其早死。未知其有可传之实。呜呼。君山之夙成。亦可谓其不幸也已。然彼世人者。既不知诗。则其不许君山。固也无足可责。而独其如靖夏者。既知其可传之实矣。犹畏俗人之为言。不图其传而遂使泯没。则岂不为深负君山于九原耶。君山之新殁。靖夏欲写取其诗一本藏之。既又思之。非所以广传之道。故遂止不为。而又欲与同志之士。谋得芸阁活字。印出其集。一以力绵而止。一以畏俗言而止。后闻执事受命西藩。则谋所以传君山之诗者。靖夏与同志者。辄相喜贺。以为君山当自此不死也。迄至于今。未有闻焉。岂亦尝有谓执事以君山诗为不当传。如向俗子之云云。而执事之中止。又如靖夏辈之畏俗言乎。若是则君山之诗。无时可传也。昔苏子美之死。其舅杜祁公为收其遗藁。欧阳公取而品题曰。斯文金玉也。于是子美之诗。遂行于天下。夫使子美不死者。乃祁公收之之力。而欧公扬之之盛也。今靖夏之言。不足以当欧公之言之重。然君山之才。无愧于子美。执事之知君山。
以过人者。及其为诗。最费深思苦吟。必欧出其肝肺而后乃止。故每一篇出。使世之能诗者尽废。然其才夙成。未克卒业而死。故世人于君山之诗。徒见其早死。未知其有可传之实。呜呼。君山之夙成。亦可谓其不幸也已。然彼世人者。既不知诗。则其不许君山。固也无足可责。而独其如靖夏者。既知其可传之实矣。犹畏俗人之为言。不图其传而遂使泯没。则岂不为深负君山于九原耶。君山之新殁。靖夏欲写取其诗一本藏之。既又思之。非所以广传之道。故遂止不为。而又欲与同志之士。谋得芸阁活字。印出其集。一以力绵而止。一以畏俗言而止。后闻执事受命西藩。则谋所以传君山之诗者。靖夏与同志者。辄相喜贺。以为君山当自此不死也。迄至于今。未有闻焉。岂亦尝有谓执事以君山诗为不当传。如向俗子之云云。而执事之中止。又如靖夏辈之畏俗言乎。若是则君山之诗。无时可传也。昔苏子美之死。其舅杜祁公为收其遗藁。欧阳公取而品题曰。斯文金玉也。于是子美之诗。遂行于天下。夫使子美不死者。乃祁公收之之力。而欧公扬之之盛也。今靖夏之言。不足以当欧公之言之重。然君山之才。无愧于子美。执事之知君山。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3L 页
 亦不下于祁公之于子美。而子美之诗。能行于流离摈斥忧谗畏忌之馀。而君山之诗。不得行于平时。呜呼。君山何其若遇而不遇也。且君山早殁。其才不能以自见于世。独其所为文章。少为人知。当其尽力为此时。意在于必传。今世知君山之不为庸人者盖鲜。若又并与其诗而泯没。则是君山之生与死。终不幸也。君山之诗之可传。靖夏请以身任之。伏惟执事深览古人爱才之意。毋畏区区妄男子之为言。亟取其诗印行。以慰君山长逝者心。则凡在平日与君山交游者。庶有以逃其责焉。今其诗若干卷。缮写一本。在君山友人处。如获印可。当令驰上。干冒尊严。无任战悚。伏惟鉴察。不宣。
亦不下于祁公之于子美。而子美之诗。能行于流离摈斥忧谗畏忌之馀。而君山之诗。不得行于平时。呜呼。君山何其若遇而不遇也。且君山早殁。其才不能以自见于世。独其所为文章。少为人知。当其尽力为此时。意在于必传。今世知君山之不为庸人者盖鲜。若又并与其诗而泯没。则是君山之生与死。终不幸也。君山之诗之可传。靖夏请以身任之。伏惟执事深览古人爱才之意。毋畏区区妄男子之为言。亟取其诗印行。以慰君山长逝者心。则凡在平日与君山交游者。庶有以逃其责焉。今其诗若干卷。缮写一本。在君山友人处。如获印可。当令驰上。干冒尊严。无任战悚。伏惟鉴察。不宣。答柳默守书
数日之间。叠辱长牍。辞旨既勤。宠与愈隆。自惟无状不肖。百无一可。而执事独以为不可弃。反覆诲谕。若此其勤者何也。岂非古人所谓诱之欲其至。于是乎愧惧惭汗。弥日不自胜。靖夏自幼读古人书。私所嗜好。窃在文章。以为才之敏钝。虽不无古今之别。而有不为声名禄利动其心者。勉之或可至。故于是乃敢发愤肆力焉。虽古人用心处。遽未可谓尽得。而乃其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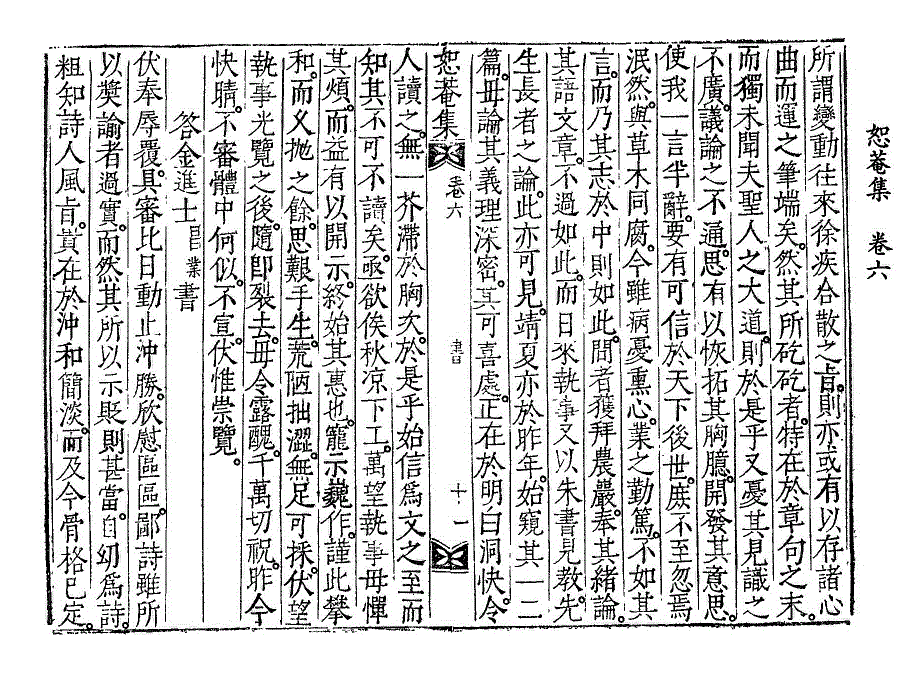 所谓变动往来徐疾合散之旨。则亦或有以存诸心曲而运之笔端矣。然其所矻矻者。特在于章句之末。而独未闻夫圣人之大道。则于是乎又忧其见识之不广。议论之不通。思有以恢拓其胸臆。开发其意思。使我一言半辞。要有可信于天下后世。庶不至忽焉泯然。与草木同腐。今虽病忧熏心。业之勤笃。不如其言。而乃其志于中则如此。间者获拜农岩。奉其绪论。其语文章。不过如此。而日来执事又以朱书见教。先生长者之论。此亦可见。靖夏亦于昨年。始窥其一二篇。毋论其义理深密。其可喜处。正在于明白洞快。令人读之。无一芥滞于胸次。于是乎始信为文之至而知其不可不读矣。亟欲俟秋凉下工。万望执事毋惮其烦。而益有以开示。终始其惠也。宠示巍作。谨此攀和。而久抛之馀。思艰手生。荒陋拙涩。无足可采。伏望执事光览之后。随即裂去。毋令露丑。千万切祝。昨今快晴。不审体中何似。不宣。伏惟崇览。
所谓变动往来徐疾合散之旨。则亦或有以存诸心曲而运之笔端矣。然其所矻矻者。特在于章句之末。而独未闻夫圣人之大道。则于是乎又忧其见识之不广。议论之不通。思有以恢拓其胸臆。开发其意思。使我一言半辞。要有可信于天下后世。庶不至忽焉泯然。与草木同腐。今虽病忧熏心。业之勤笃。不如其言。而乃其志于中则如此。间者获拜农岩。奉其绪论。其语文章。不过如此。而日来执事又以朱书见教。先生长者之论。此亦可见。靖夏亦于昨年。始窥其一二篇。毋论其义理深密。其可喜处。正在于明白洞快。令人读之。无一芥滞于胸次。于是乎始信为文之至而知其不可不读矣。亟欲俟秋凉下工。万望执事毋惮其烦。而益有以开示。终始其惠也。宠示巍作。谨此攀和。而久抛之馀。思艰手生。荒陋拙涩。无足可采。伏望执事光览之后。随即裂去。毋令露丑。千万切祝。昨今快晴。不审体中何似。不宣。伏惟崇览。答金进士(昌业)书
伏奉辱覆。具审比日动止冲胜。欣慰区区。鄙诗虽所以奖谕者过实。而然其所以示贬则甚当。自幼为诗。粗知诗人风旨。贵在于冲和简淡。而及今骨格已定。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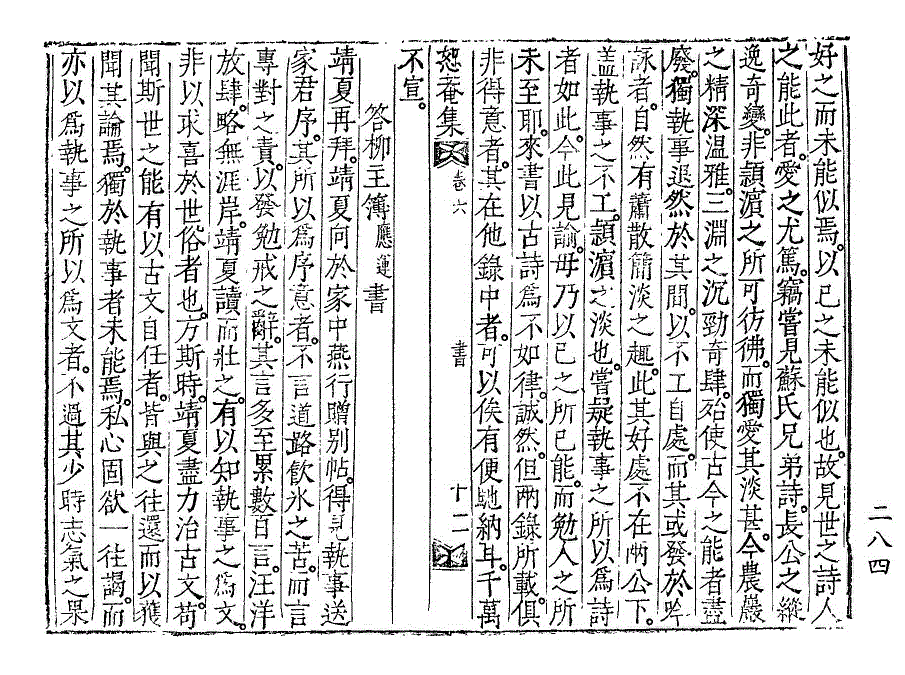 好之而未能似焉。以己之未能似也。故见世之诗人之能此者。爱之尤笃。窃尝见苏氏兄弟诗。长公之纵逸奇变。非颖滨之所可彷佛。而独爱其淡甚。今农岩之精深温雅。三渊之沉劲奇肆。殆使古今之能者尽废。独执事退然于其间。以不工自处。而其或发于吟咏者。自然有萧散简淡之趣。此其好处不在两公下。盖执事之不工。颖滨之淡也。尝疑执事之所以为诗者如此。今此见谕。毋乃以己之所已能。而勉人之所未至耶。来书以古诗为不如律。诚然。但两录所载。俱非得意者。其在他录中者。可以俟有便驰纳耳。千万不宣。
好之而未能似焉。以己之未能似也。故见世之诗人之能此者。爱之尤笃。窃尝见苏氏兄弟诗。长公之纵逸奇变。非颖滨之所可彷佛。而独爱其淡甚。今农岩之精深温雅。三渊之沉劲奇肆。殆使古今之能者尽废。独执事退然于其间。以不工自处。而其或发于吟咏者。自然有萧散简淡之趣。此其好处不在两公下。盖执事之不工。颖滨之淡也。尝疑执事之所以为诗者如此。今此见谕。毋乃以己之所已能。而勉人之所未至耶。来书以古诗为不如律。诚然。但两录所载。俱非得意者。其在他录中者。可以俟有便驰纳耳。千万不宣。答柳主簿(应运)书
靖夏再拜。靖夏向于家中燕行赠别帖。得见执事送家君序。其所以为序意者。不言道路饮冰之苦。而言专对之责。以发勉戒之辞。其言多至累数百言。汪洋放肆。略无涯岸。靖夏读而壮之。有以知执事之为文。非以求喜于世俗者也。方斯时。靖夏尽力治古文。苟闻斯世之能有以古文自任者。皆与之往还而以获闻其论焉。独于执事者未能焉。私心固欲一往谒。而亦以为执事之所以为文者。不过其少时志气之果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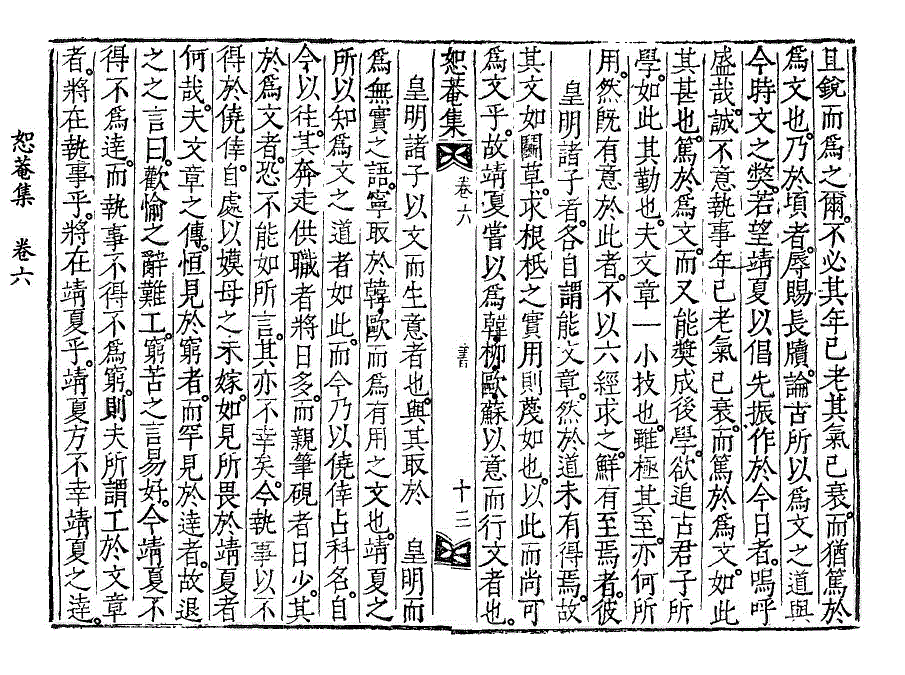 且锐而为之尔。不必其年已老其气已衰。而犹笃于为文也。乃于顷者。辱赐长牍。论古所以为文之道与今时文之弊。若望靖夏以倡先振作于今日者。呜呼盛哉。诚不意执事年已老气已衰。而笃于为文。如此其甚也。笃于为文。而又能奖成后学。欲追古君子所学。如此其勤也。夫文章一小技也。虽极其至。亦何所用。然既有意于此者。不以六经求之。鲜有至焉者。彼 皇明诸子者。各自谓能文章。然于道未有得焉。故其文如斗草。求根柢之实用则蔑如也。以此而尚可为文乎。故靖夏尝以为韩,柳,欧,苏以意而行文者也。 皇明诸子以文而生意者也。与其取于 皇明而为无实之语。宁取于韩,欧而为有用之文也。靖夏之所以知为文之道者如此。而今乃以侥倖占科名。自今以往。其奔走供职者将日多。而亲笔砚者日少。其于为文者。恐不能如所言。其亦不幸矣。今执事以不得于侥倖。自处以嫫母之未嫁。如见所畏于靖夏者何哉。夫文章之传。恒见于穷者。而罕见于达者。故退之之言曰。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今靖夏不得不为达。而执事不得不为穷。则夫所谓工于文章者。将在执事乎。将在靖夏乎。靖夏方不幸靖夏之达。
且锐而为之尔。不必其年已老其气已衰。而犹笃于为文也。乃于顷者。辱赐长牍。论古所以为文之道与今时文之弊。若望靖夏以倡先振作于今日者。呜呼盛哉。诚不意执事年已老气已衰。而笃于为文。如此其甚也。笃于为文。而又能奖成后学。欲追古君子所学。如此其勤也。夫文章一小技也。虽极其至。亦何所用。然既有意于此者。不以六经求之。鲜有至焉者。彼 皇明诸子者。各自谓能文章。然于道未有得焉。故其文如斗草。求根柢之实用则蔑如也。以此而尚可为文乎。故靖夏尝以为韩,柳,欧,苏以意而行文者也。 皇明诸子以文而生意者也。与其取于 皇明而为无实之语。宁取于韩,欧而为有用之文也。靖夏之所以知为文之道者如此。而今乃以侥倖占科名。自今以往。其奔走供职者将日多。而亲笔砚者日少。其于为文者。恐不能如所言。其亦不幸矣。今执事以不得于侥倖。自处以嫫母之未嫁。如见所畏于靖夏者何哉。夫文章之传。恒见于穷者。而罕见于达者。故退之之言曰。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今靖夏不得不为达。而执事不得不为穷。则夫所谓工于文章者。将在执事乎。将在靖夏乎。靖夏方不幸靖夏之达。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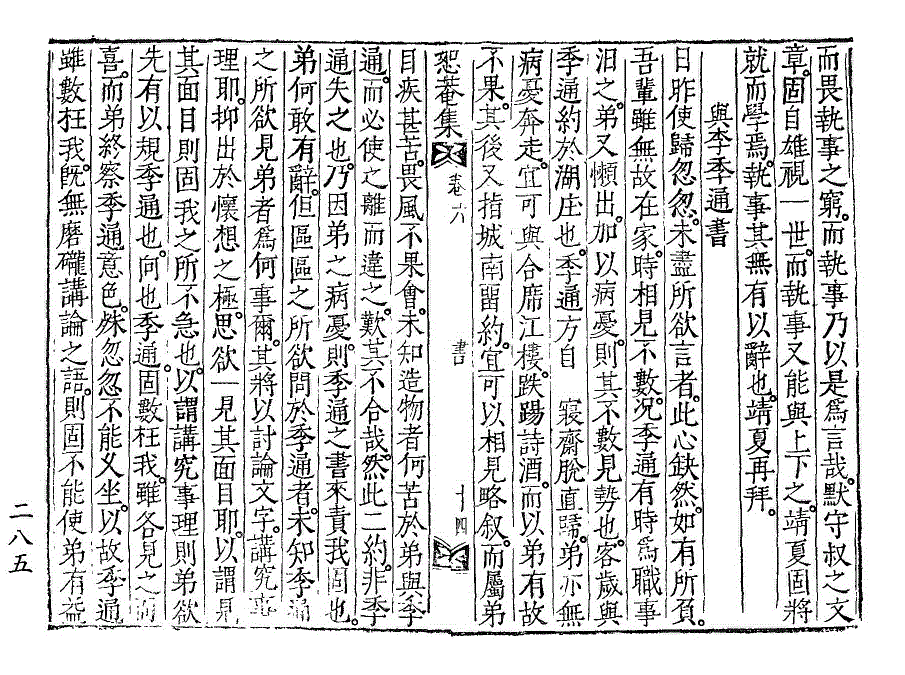 而畏执事之穷。而执事乃以是为言哉。默守叔之文章。固自雄视一世。而执事又能与上下之。靖夏固将就而学焉。执事其无有以辞也。靖夏再拜。
而畏执事之穷。而执事乃以是为言哉。默守叔之文章。固自雄视一世。而执事又能与上下之。靖夏固将就而学焉。执事其无有以辞也。靖夏再拜。与李季通书
日昨使归匆匆。未尽所欲言者。此心缺然。如有所负。吾辈虽无故在家。时相见不数。况季通有时为职事汨之。弟又懒出。加以病忧。则其不数见势也。客岁与季通约于湖庄也。季通方自 寝斋脱直归。弟亦无病忧奔走。宜可与合席江楼。跌踼诗酒。而以弟有故不果。其后又指城南留约。宜可以相见略叙。而属弟目疾甚苦。畏风不果会。未知造物者何苦于弟与季通。而必使之离而违之。叹其不合哉。然此二约。非季通失之也。乃因弟之病忧。则季通之书来责我固也。弟何敢有辞。但区区之所欲问于季通者。未知季通之所欲见弟者为何事尔。其将以讨论文字。讲究事理耶。抑出于怀想之极。思欲一见其面目耶。以谓见其面目则固我之所不急也。以谓讲究事理则弟欲先有以规季通也。向也季通。固数枉我。虽各见之而喜。而弟终察季通意色。殊忽忽不能久坐。以故季通虽数枉我。既无磨砻讲论之语。则固不能使弟有益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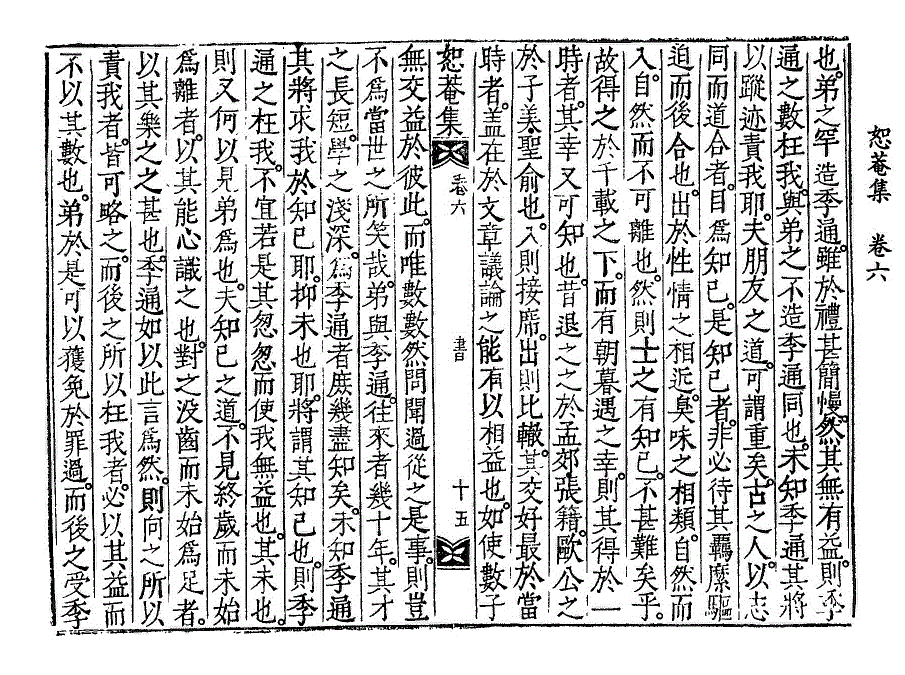 也。弟之罕造季通。虽于礼甚简慢。然其无有益。则季通之数枉我。与弟之不造季通同也。未知季通其将以踪迹责我耶。夫朋友之道。可谓重矣。古之人。以志同而道合者。目为知己。是知己者。非必待其羁縻驱迫而后合也。出于性情之相近。臭味之相类。自然而入。自然而不可离也。然则士之有知己。不甚难矣乎。故得之于千载之下。而有朝暮遇之幸。则其得于一时者。其幸又可知也。昔退之之于孟郊,张籍。欧公之于子美,圣俞也。入则接席。出则比辙。其交好最于当时者。盖在于文章议论之能有以相益也。如使数子无交益于彼此。而唯数数然问闻过从之是事。则岂不为当世之所笑哉。弟与季通。往来者几十年。其才之长短。学之浅深。为季通者庶几尽知矣。未知季通其将求我于知己耶。抑未也耶。将谓其知己也。则季通之枉我。不宜若是其匆匆而使我无益也。其未也。则又何以见弟为也。夫知己之道。不见终岁而未始为离者。以其能心识之也。对之没齿而未始为足者。以其乐之之甚也。季通如以此言为然。则向之所以责我者。皆可略之。而后之所以枉我者。必以其益而不以其数也。弟于是可以获免于罪过。而后之受季
也。弟之罕造季通。虽于礼甚简慢。然其无有益。则季通之数枉我。与弟之不造季通同也。未知季通其将以踪迹责我耶。夫朋友之道。可谓重矣。古之人。以志同而道合者。目为知己。是知己者。非必待其羁縻驱迫而后合也。出于性情之相近。臭味之相类。自然而入。自然而不可离也。然则士之有知己。不甚难矣乎。故得之于千载之下。而有朝暮遇之幸。则其得于一时者。其幸又可知也。昔退之之于孟郊,张籍。欧公之于子美,圣俞也。入则接席。出则比辙。其交好最于当时者。盖在于文章议论之能有以相益也。如使数子无交益于彼此。而唯数数然问闻过从之是事。则岂不为当世之所笑哉。弟与季通。往来者几十年。其才之长短。学之浅深。为季通者庶几尽知矣。未知季通其将求我于知己耶。抑未也耶。将谓其知己也。则季通之枉我。不宜若是其匆匆而使我无益也。其未也。则又何以见弟为也。夫知己之道。不见终岁而未始为离者。以其能心识之也。对之没齿而未始为足者。以其乐之之甚也。季通如以此言为然。则向之所以责我者。皆可略之。而后之所以枉我者。必以其益而不以其数也。弟于是可以获免于罪过。而后之受季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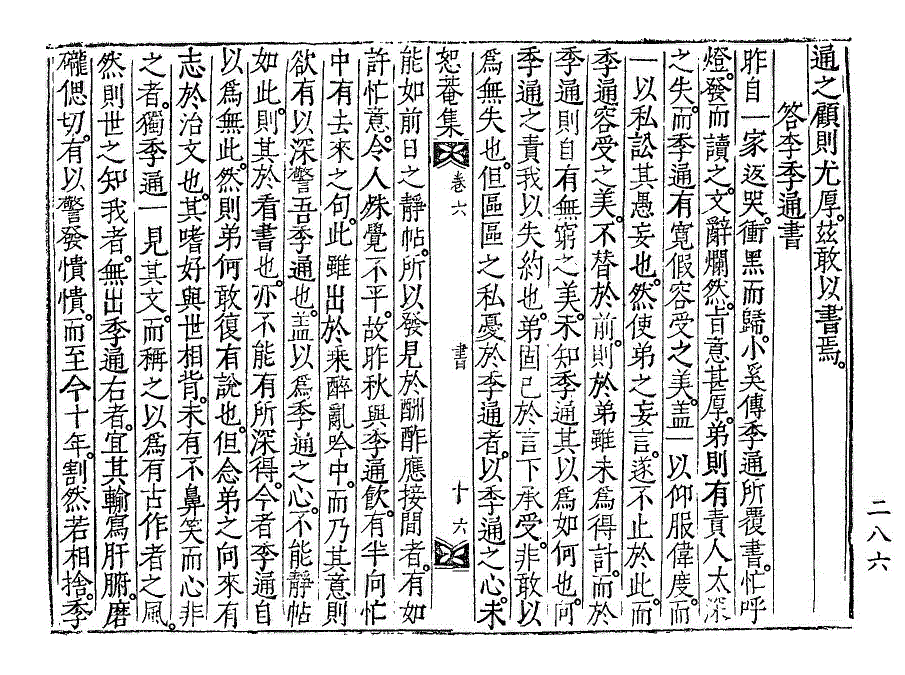 通之顾则尤厚。玆敢以书焉。
通之顾则尤厚。玆敢以书焉。答李季通书
昨自一家返哭。冲黑而归。小奚传季通所覆书。忙呼灯。发而读之。文辞烂然。旨意甚厚。弟则有责人太深之失。而季通有宽假容受之美。盖一以仰服伟度。而一以私讼其愚妄也。然使弟之妄言。遂不止于此。而季通容受之美。不替于前。则于弟虽未为得计。而于季通则自有无穷之美。未知季通其以为如何也。向季通之责我以失约也。弟固已于言下承受。非敢以为无失也。但区区之私忧于季通者。以季通之心。未能如前日之静帖。所以发见于酬酢应接间者。有如许忙意。令人殊觉不平。故昨秋与季通饮。有半向忙中有去来之句。此虽出于乘醉乱吟中。而乃其意则欲有以深警吾季通也。盖以为季通之心。不能静帖如此。则其于看书也。亦不能有所深得。今者季通自以为无此。然则弟何敢复有说也。但念弟之向来有志于治文也。其嗜好与世相背。未有不鼻笑而心非之者。独季通一见其文。而称之以为有古作者之风。然则世之知我者。无出季通右者。宜其输写肝腑。磨砻偲切。有以警发愦愦。而至今十年。割然若相舍。季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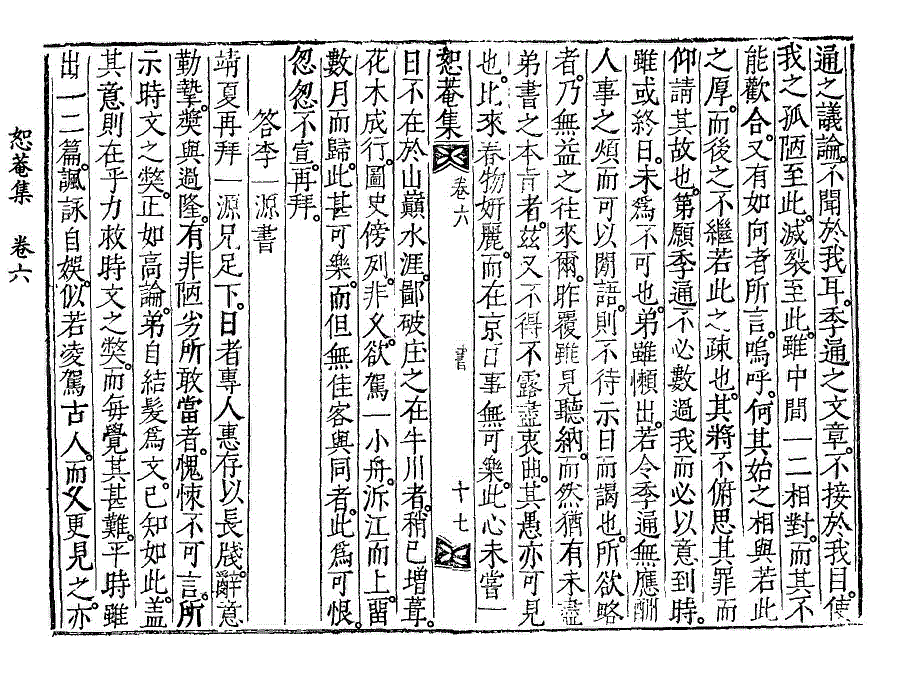 通之议论。不闻于我耳。季通之文章。不接于我目。使我之孤陋至此。灭裂至此。虽中间一二相对。而其不能欢合。又有如向者所言。呜呼。何其始之相与若此之厚。而后之不继若此之疏也。其将不俯思其罪而仰请其故也。第愿季通不必数过我而必以意到时。虽或终日。未为不可也。弟虽懒出。若令季通无应酬人事之烦而可以閒语。则不待示日而谒也。所欲略者。乃无益之往来尔。昨覆虽见听纳。而然犹有未尽弟书之本旨者。玆又不得不露尽衷曲。其愚亦可见也。比来春物妍丽。而在京百事无可乐。此心未尝一日不在于山巅水涯。鄙破庄之在牛川者。稍已增葺。花木成行。图史傍列。非久。欲驾一小舟。溯江而上。留数月而归。此甚可乐。而但无佳客与同者。此为可恨。匆匆不宣。再拜。
通之议论。不闻于我耳。季通之文章。不接于我目。使我之孤陋至此。灭裂至此。虽中间一二相对。而其不能欢合。又有如向者所言。呜呼。何其始之相与若此之厚。而后之不继若此之疏也。其将不俯思其罪而仰请其故也。第愿季通不必数过我而必以意到时。虽或终日。未为不可也。弟虽懒出。若令季通无应酬人事之烦而可以閒语。则不待示日而谒也。所欲略者。乃无益之往来尔。昨覆虽见听纳。而然犹有未尽弟书之本旨者。玆又不得不露尽衷曲。其愚亦可见也。比来春物妍丽。而在京百事无可乐。此心未尝一日不在于山巅水涯。鄙破庄之在牛川者。稍已增葺。花木成行。图史傍列。非久。欲驾一小舟。溯江而上。留数月而归。此甚可乐。而但无佳客与同者。此为可恨。匆匆不宣。再拜。答李一源书
靖夏再拜一源兄足下。日者专人惠存以长笺。辞意勤挚。奖与过隆。有非陋劣所敢当者。愧悚不可言。所示时文之弊。正如高论。弟自结发为文。已知如此。盖其意则在乎力救时文之弊。而每觉其甚难。平时虽出一二篇。讽咏自娱。似若凌驾古人。而久更见之。亦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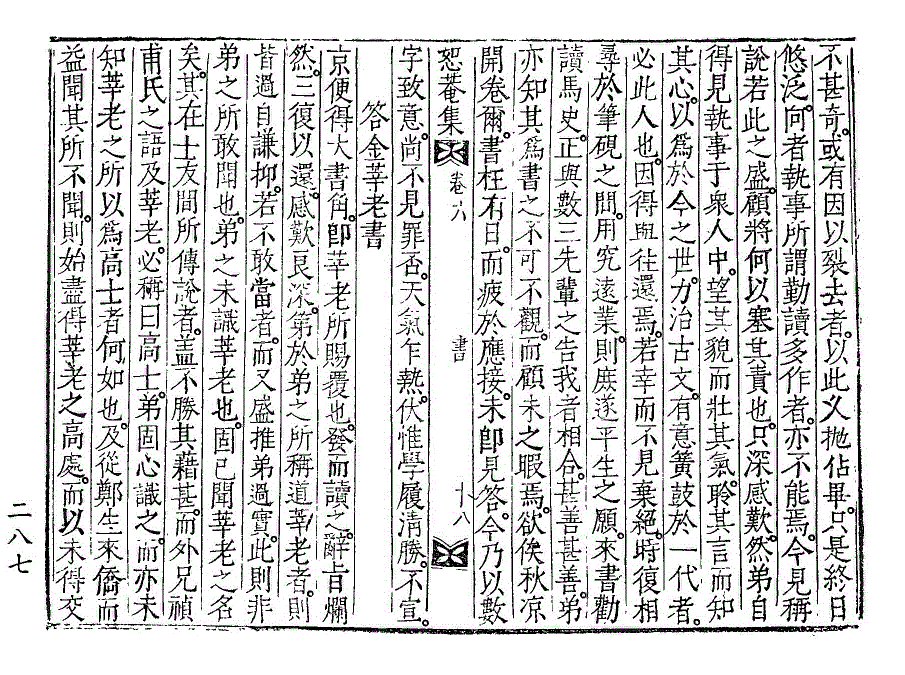 不甚奇。或有因以裂去者。以此久抛佔毕。只是终日悠泛。向者执事所谓勤读多作者。亦不能焉。今见称说若此之盛。顾将何以塞其责也。只深感叹。然弟自得见执事于众人中。望其貌而壮其气。聆其言而知其心。以为于今之世。力治古文。有意簧鼓于一代者。必此人也。因得与往还焉。若幸而不见弃绝。时复相寻于笔砚之间。用究远业。则庶遂平生之愿。来书劝读马史。正与数三先辈之告我者相合。甚善甚善。弟亦知其为书之不可不观。而顾未之暇焉。欲俟秋凉开卷尔。书枉有日。而疲于应接。未即见答。今乃以数字致意。尚不见罪否。天气乍热。伏惟学履清胜。不宣。
不甚奇。或有因以裂去者。以此久抛佔毕。只是终日悠泛。向者执事所谓勤读多作者。亦不能焉。今见称说若此之盛。顾将何以塞其责也。只深感叹。然弟自得见执事于众人中。望其貌而壮其气。聆其言而知其心。以为于今之世。力治古文。有意簧鼓于一代者。必此人也。因得与往还焉。若幸而不见弃绝。时复相寻于笔砚之间。用究远业。则庶遂平生之愿。来书劝读马史。正与数三先辈之告我者相合。甚善甚善。弟亦知其为书之不可不观。而顾未之暇焉。欲俟秋凉开卷尔。书枉有日。而疲于应接。未即见答。今乃以数字致意。尚不见罪否。天气乍热。伏惟学履清胜。不宣。答金莘老书
京便得大书角。即莘老所赐覆也。发而读之。辞旨烂然。三复以还。感叹良深。第于弟之所称道莘老者。则皆过自谦抑。若不敢当者。而又盛推弟过实。此则非弟之所敢闻也。弟之未识莘老也。固已闻莘老之名矣。其在士友间所传说者。盖不胜其藉甚。而外兄祯甫氏之语及莘老。必称曰高士。弟固心识之。而亦未知莘老之所以为高士者何如也。及从郑生来侨而益闻其所不闻。则始尽得莘老之高处。而以未得交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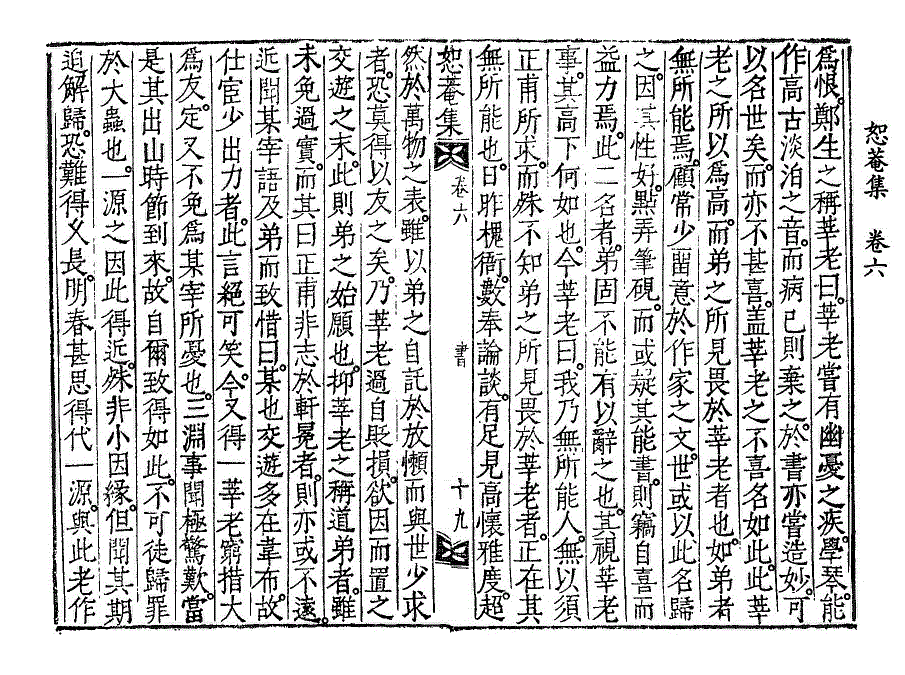 为恨。郑生之称莘老曰。莘老尝有幽忧之疾。学琴。能作高古淡泊之音。而病已则弃之。于书亦尝造妙。可以名世矣。而亦不甚喜。盖莘老之不喜名如此。此莘老之所以为高。而弟之所见畏于莘老者也。如弟者无所能焉。顾常少留意于作家之文。世或以此名归之。因其性好。点弄笔砚。而或疑其能书。则窃自喜而益力焉。此二名者。弟固不能有以辞之也。其视莘老事。其高下何如也。今莘老曰。我乃无所能人。无以须正甫所求。而殊不知弟之所见畏于莘老者。正在其无所能也。日昨槐衙。数奉论谈。有足见高怀雅度。超然于万物之表。虽以弟之自托于放懒而与世少求者。恐莫得以友之矣。乃莘老过自贬损。欲因而置之交游之末。此则弟之始愿也。抑莘老之称道弟者。虽未免过实。而其曰正甫非志于轩冕者。则亦或不远。近闻某宰语及弟而致惜曰。某也交游多在韦布。故仕宦少出力者。此言绝可笑。今又得一莘老穷措大为友。定又不免为某宰所忧也。三渊事闻极惊叹。当是其出山时节到来。故自尔致得如此。不可徒归罪于大虫也。一源之因此得近。殊非小因缘。但闻其期迫解归。恐难得久长。明春甚思得代一源。与此老作
为恨。郑生之称莘老曰。莘老尝有幽忧之疾。学琴。能作高古淡泊之音。而病已则弃之。于书亦尝造妙。可以名世矣。而亦不甚喜。盖莘老之不喜名如此。此莘老之所以为高。而弟之所见畏于莘老者也。如弟者无所能焉。顾常少留意于作家之文。世或以此名归之。因其性好。点弄笔砚。而或疑其能书。则窃自喜而益力焉。此二名者。弟固不能有以辞之也。其视莘老事。其高下何如也。今莘老曰。我乃无所能人。无以须正甫所求。而殊不知弟之所见畏于莘老者。正在其无所能也。日昨槐衙。数奉论谈。有足见高怀雅度。超然于万物之表。虽以弟之自托于放懒而与世少求者。恐莫得以友之矣。乃莘老过自贬损。欲因而置之交游之末。此则弟之始愿也。抑莘老之称道弟者。虽未免过实。而其曰正甫非志于轩冕者。则亦或不远。近闻某宰语及弟而致惜曰。某也交游多在韦布。故仕宦少出力者。此言绝可笑。今又得一莘老穷措大为友。定又不免为某宰所忧也。三渊事闻极惊叹。当是其出山时节到来。故自尔致得如此。不可徒归罪于大虫也。一源之因此得近。殊非小因缘。但闻其期迫解归。恐难得久长。明春甚思得代一源。与此老作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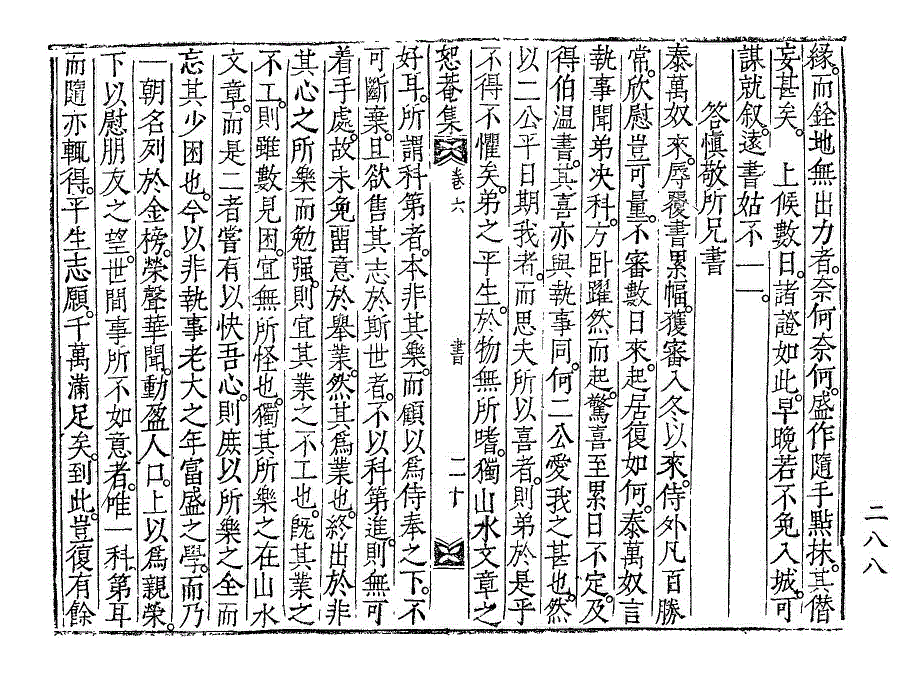 缘。而铨地无出力者。奈何奈何。盛作随手点抹。其僭妄甚矣。 上候数日。诸證如此。早晚若不免入城。可谋就叙。远书姑不一一。
缘。而铨地无出力者。奈何奈何。盛作随手点抹。其僭妄甚矣。 上候数日。诸證如此。早晚若不免入城。可谋就叙。远书姑不一一。答慎敬所兄书
泰万奴来。辱覆书累幅。获审入冬以来。侍外凡百胜常。欣慰岂可量。不审数日来。起居复如何。泰万奴言执事闻弟决科。方卧跃然而起。惊喜至累日不定。及得伯温书。其喜亦与执事同。何二公爱我之甚也。然以二公平日期我者。而思夫所以喜者。则弟于是乎不得不惧矣。弟之平生。于物无所嗜。独山水文章之好耳。所谓科第者。本非其乐。而顾以为侍奉之下。不可断弃。且欲售其志于斯世者。不以科第进。则无可着手处。故未免留意于举业。然其为业也。终出于非其心之所乐而勉强。则宜其业之不工也。既其业之不工。则虽数见困。宜无所怪也。独其所乐之在山水文章。而是二者尝有以快吾心。则庶以所乐之全而忘其少困也。今以非执事老大之年富盛之学。而乃一朝名列于金榜。荣声华闻。动盈人口。上以为亲荣。下以慰朋友之望。世间事所不如意者。唯一科第耳而随亦辄得。平生志愿。千万满足矣。到此。岂复有馀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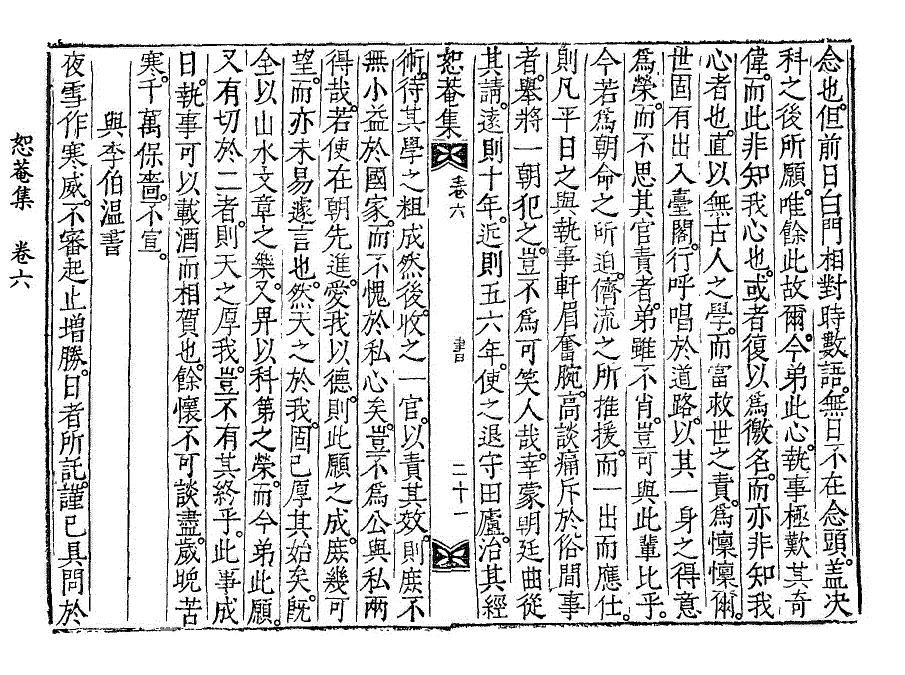 念也。但前日白门相对时数语。无日不在念头。盖决科之后所愿。唯馀此故尔。今弟此心。执事极叹其奇伟。而此非知我心也。或者复以为徼名。而亦非知我心者也。直以无古人之学。而当救世之责。为懔懔尔。世固有出入台阁。行呼唱于道路。以其一身之得意为荣。而不思其官责者。弟虽不肖。岂可与此辈比乎。今若为朝命之所迫。侪流之所推援。而一出而应仕。则凡平日之与执事轩眉奋腕。高谈痛斥于俗间事者。举将一朝犯之。岂不为可笑人哉。幸蒙朝廷曲从其请。远则十年。近则五六年。使之退守田庐。治其经术。待其学之粗成然后。收之一官。以责其效。则庶不无小益于国家。而不愧于私心矣。岂不为公与私两得哉。若使在朝先进。爱我以德。则此愿之成。庶几可望。而亦未易遽言也。然天之于我。固已厚其始矣。既全以山水文章之乐。又畀以科第之荣。而今弟此愿。又有切于二者。则天之厚我。岂不有其终乎。此事成日。执事可以载酒而相贺也。馀怀不可谈尽。岁晚苦寒。千万保啬。不宣。
念也。但前日白门相对时数语。无日不在念头。盖决科之后所愿。唯馀此故尔。今弟此心。执事极叹其奇伟。而此非知我心也。或者复以为徼名。而亦非知我心者也。直以无古人之学。而当救世之责。为懔懔尔。世固有出入台阁。行呼唱于道路。以其一身之得意为荣。而不思其官责者。弟虽不肖。岂可与此辈比乎。今若为朝命之所迫。侪流之所推援。而一出而应仕。则凡平日之与执事轩眉奋腕。高谈痛斥于俗间事者。举将一朝犯之。岂不为可笑人哉。幸蒙朝廷曲从其请。远则十年。近则五六年。使之退守田庐。治其经术。待其学之粗成然后。收之一官。以责其效。则庶不无小益于国家。而不愧于私心矣。岂不为公与私两得哉。若使在朝先进。爱我以德。则此愿之成。庶几可望。而亦未易遽言也。然天之于我。固已厚其始矣。既全以山水文章之乐。又畀以科第之荣。而今弟此愿。又有切于二者。则天之厚我。岂不有其终乎。此事成日。执事可以载酒而相贺也。馀怀不可谈尽。岁晚苦寒。千万保啬。不宣。与李伯温书
夜雪作寒威。不审起止增胜。日者所托。谨已具问于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89L 页
 局中解事吏。且于别纸。录奉其资级年齿。幸赐览阅焉。闻此人等当初以都监炮手下番。在高阳郡。而方是时。仆高祖忠翼公为训局大将。及丙子之乱。忠翼公以本局兵。扈 仁庙于南汉。而此人等与焉。悔祸之初。凡百馀人。各以其劳受爵禄。六十年之间。皆已老死。而存者仅十人。每 上诞节。十人者犹能扶杖诣阙下。问候于 上。自 上以酒肉馈之。俱各尽醉扶携而归。又以其馀。及于子孙。以为荣焉。盖其闻得于局吏者。其始末如此。惜也。当干戈抢攘之际。 玉辇蒙尘之日。此辈俱甘心于肝脑之涂地。而以赤心奉 上。意其变乱仓卒之中。毋论斩获与俘虏。必有一二奇功可闻者。而老者既神耗不能言。其子孙又不足知。此为可恨。但弟之问此事于局吏也。同知严起生者。闻风强起。来见弟。弟问以向时事。则亦不能答。良久。但拊膺叹曰。此身所以登矢石之场而受枪刃之苦。得一生于百死而以重见 圣世者。顾有幸存焉耳。独记城上之战。 圣上日夜涕泣申命曰。而各用而心。无以苦为也。予归他日。毋忘而劳也。今不复得闻此语矣。因感激泪下。弟闻比者地部急于省费。于十人者。亦减其衣资料米。岂此老之言。因今日
局中解事吏。且于别纸。录奉其资级年齿。幸赐览阅焉。闻此人等当初以都监炮手下番。在高阳郡。而方是时。仆高祖忠翼公为训局大将。及丙子之乱。忠翼公以本局兵。扈 仁庙于南汉。而此人等与焉。悔祸之初。凡百馀人。各以其劳受爵禄。六十年之间。皆已老死。而存者仅十人。每 上诞节。十人者犹能扶杖诣阙下。问候于 上。自 上以酒肉馈之。俱各尽醉扶携而归。又以其馀。及于子孙。以为荣焉。盖其闻得于局吏者。其始末如此。惜也。当干戈抢攘之际。 玉辇蒙尘之日。此辈俱甘心于肝脑之涂地。而以赤心奉 上。意其变乱仓卒之中。毋论斩获与俘虏。必有一二奇功可闻者。而老者既神耗不能言。其子孙又不足知。此为可恨。但弟之问此事于局吏也。同知严起生者。闻风强起。来见弟。弟问以向时事。则亦不能答。良久。但拊膺叹曰。此身所以登矢石之场而受枪刃之苦。得一生于百死而以重见 圣世者。顾有幸存焉耳。独记城上之战。 圣上日夜涕泣申命曰。而各用而心。无以苦为也。予归他日。毋忘而劳也。今不复得闻此语矣。因感激泪下。弟闻比者地部急于省费。于十人者。亦减其衣资料米。岂此老之言。因今日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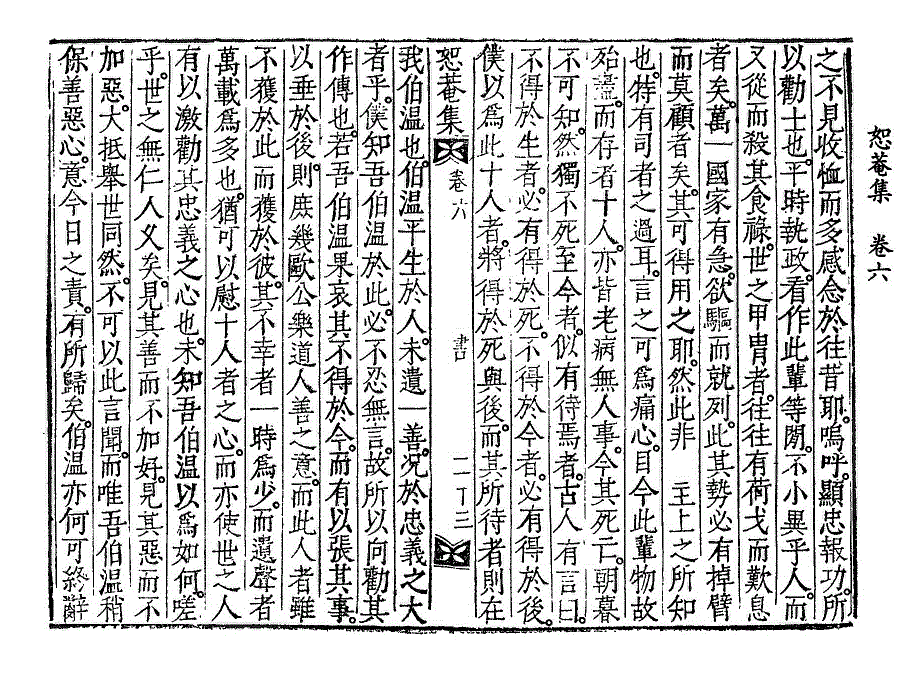 之不见收恤而多感念于往昔耶。呜呼。显忠报功。所以劝士也。平时执政。看作此辈等閒。不小异乎人。而又从而杀其食禄。世之甲冑者。往往有荷戈而叹息者矣。万一国家有急。欲驱而就列。此其势必有掉臂而莫顾者矣。其可得用之耶。然此非 主上之所知也。特有司者之过耳。言之可为痛心。目今此辈物故殆尽。而存者十人。亦皆老病无人事。今其死亡。朝暮不可知。然独不死至今者。似有待焉者。古人有言曰。不得于生者。必有得于死。不得于今者。必有得于后。仆以为此十人者。将得于死与后。而其所待者则在我伯温也。伯温平生于人。未遗一善。况于忠义之大者乎。仆知吾伯温于此。必不忍无言。故所以向劝其作传也。若吾伯温果哀其不得于今。而有以张其事。以垂于后。则庶几欧公乐道人善之意。而此人者虽不获于此而获于彼。其不幸者一时为少。而遗声者万载为多也。犹可以慰十人者之心。而亦使世之人有以激劝其忠义之心也。未知吾伯温以为如何。嗟乎。世之无仁人久矣。见其善而不加好。见其恶而不加恶。大抵举世同然。不可以此言闻。而唯吾伯温稍保善恶心。意今日之责。有所归矣。伯温亦何可终辞
之不见收恤而多感念于往昔耶。呜呼。显忠报功。所以劝士也。平时执政。看作此辈等閒。不小异乎人。而又从而杀其食禄。世之甲冑者。往往有荷戈而叹息者矣。万一国家有急。欲驱而就列。此其势必有掉臂而莫顾者矣。其可得用之耶。然此非 主上之所知也。特有司者之过耳。言之可为痛心。目今此辈物故殆尽。而存者十人。亦皆老病无人事。今其死亡。朝暮不可知。然独不死至今者。似有待焉者。古人有言曰。不得于生者。必有得于死。不得于今者。必有得于后。仆以为此十人者。将得于死与后。而其所待者则在我伯温也。伯温平生于人。未遗一善。况于忠义之大者乎。仆知吾伯温于此。必不忍无言。故所以向劝其作传也。若吾伯温果哀其不得于今。而有以张其事。以垂于后。则庶几欧公乐道人善之意。而此人者虽不获于此而获于彼。其不幸者一时为少。而遗声者万载为多也。犹可以慰十人者之心。而亦使世之人有以激劝其忠义之心也。未知吾伯温以为如何。嗟乎。世之无仁人久矣。见其善而不加好。见其恶而不加恶。大抵举世同然。不可以此言闻。而唯吾伯温稍保善恶心。意今日之责。有所归矣。伯温亦何可终辞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0L 页
 乎。伯温谅之。
乎。伯温谅之。与李伯温书
比为人邀请。作看花寻寺之行。身不离鞍者。十馀日矣。此事本以为閒。而今反不閒。殊不如向日闭户静坐之有味也。昨从佛岩晚归。明远言伯温于其间枉此。且出读弟劝西伯梓君山诗书。有所论评。远侄虽不细传。然亦得其一二不能无疑于鄙心者。今伯温曰。君山固有磊落之气正直之论敏达之识。而正甫并不见及此。恐未喻弟书之本旨也。弟书固曰君山之才。有以过人者。又曰。今世无知君山之不为庸人。此数语。其许君山一生。已自足。但不细言之耳。若使弟言能信于后者。此数语。已于君山不薄。如其难保。虽细言奚益哉。伯温又曰。今君山之诗。稍有眼目者。爱之知之者。不为不众。其曰不知有可传之实者。非也。此却不然。伯温所谓有眼目者。指何如人也。既曰有眼目。则不为俗人。今世之知诗而精于眼目者。遂可以多于俗人乎。世之以君山诗为可传者。如李夏坤,李秉渊,李德寿,弟与伯温辈数人而已。其他所谓好君山诗者。未必真知而以为可传也。今伯温欲以世人爱好之众寡。论其诗之工拙。此非独乖剌于弟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1H 页
 心。却不似知君山者。君山平日。其诗有见喜于俗人者。甚以为可耻。有俗人之求见其诗者。辄不肯与。此曾闻于伯温者。弟以为君山之为诗。必不使人人皆喜。如伯温所言。而其诗之传不传。必不在于俗人爱好之众寡也。且闻西伯去时。以谋刻君山诗为言。今久无报者。意必有以君山诗为不当传。如书中所言。故极言其诗之必可传。俗言之不足恤。与其人早死之不幸。以相感动而劝勉之耳。今若曰一世人皆言其诗之可传。则彼必不信也。伯温又曰。君山之诗。格律深到。已自成家。虽早死。不可谓不卒业也。此又不然。君山之诗。固自老成。弟每欲学之而未得。伯温所谓成家者是也。然若使君山在。其诗遂止此而已乎。既曰不止此。其言不卒业者。未见其非也。大抵伯温以不铺张君山之为人为失。而此本劝刻其诗而作。非如记其行实之文。故并略之。只以其诗之可传而不能传为说。以发其无限慨惜。庶有以动其听耳。伯温以弟言为如何。若无事。何不一来对讨。
心。却不似知君山者。君山平日。其诗有见喜于俗人者。甚以为可耻。有俗人之求见其诗者。辄不肯与。此曾闻于伯温者。弟以为君山之为诗。必不使人人皆喜。如伯温所言。而其诗之传不传。必不在于俗人爱好之众寡也。且闻西伯去时。以谋刻君山诗为言。今久无报者。意必有以君山诗为不当传。如书中所言。故极言其诗之必可传。俗言之不足恤。与其人早死之不幸。以相感动而劝勉之耳。今若曰一世人皆言其诗之可传。则彼必不信也。伯温又曰。君山之诗。格律深到。已自成家。虽早死。不可谓不卒业也。此又不然。君山之诗。固自老成。弟每欲学之而未得。伯温所谓成家者是也。然若使君山在。其诗遂止此而已乎。既曰不止此。其言不卒业者。未见其非也。大抵伯温以不铺张君山之为人为失。而此本劝刻其诗而作。非如记其行实之文。故并略之。只以其诗之可传而不能传为说。以发其无限慨惜。庶有以动其听耳。伯温以弟言为如何。若无事。何不一来对讨。与李伯温书
至后寒甚。不审起处更如何。三洲其已往返。而冰路蹇卫。能免狼狈否。吾兄近久屈首公车。意思想必不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1L 页
 乐。昨日之行。似出于乘兴。未知长者有何言也。斯道也本为世间公物。不宜吾兄独秘而私有之。不以共人也。弟比绝不看他书。只寝饭时外。眼目专在于诗书关洛诸书。虽未敢遽曰有所得。然自觉与看韩欧辈文字时甚别。然此心之放而不知求。已积以二十年矣。今来省察。自觉病败百出。于一日接物应事上。试求此心之粹然全出于天理者。几无有焉。虽是向来之自谓处事之不苟。行己之似高。而可以无大愧于古之贤人君子者。到今思之。或出于循名。或出于为物。其幸而不至为二者之甚者。而亦不免于有意之私。可惜天生此身。其所以付托责望者。岂是草草。而只此一个心。枉用于文章。枉用于诗句。枉用于书画。枉用于科场。至今顽然为自暴自弃底人。循省汗出。未知此身。去彼两翼四足而飞走者。为几寸耳。今弟心。正如袯襫家子孙之幼失其父祖所传来许多田地第宅者。却被人诳诱。或远商客方。或寄佣他家。及其年齿之渐大饥寒之日逼然后。还归故里。徊翔踯躅。偶得其残缺文籍于坠弃之中而恍然自悟。始知我初之未尝无田地。又未尝无第宅。却自笑为何而远商客方。为何而寄佣他家。方思持是而访问。返
乐。昨日之行。似出于乘兴。未知长者有何言也。斯道也本为世间公物。不宜吾兄独秘而私有之。不以共人也。弟比绝不看他书。只寝饭时外。眼目专在于诗书关洛诸书。虽未敢遽曰有所得。然自觉与看韩欧辈文字时甚别。然此心之放而不知求。已积以二十年矣。今来省察。自觉病败百出。于一日接物应事上。试求此心之粹然全出于天理者。几无有焉。虽是向来之自谓处事之不苟。行己之似高。而可以无大愧于古之贤人君子者。到今思之。或出于循名。或出于为物。其幸而不至为二者之甚者。而亦不免于有意之私。可惜天生此身。其所以付托责望者。岂是草草。而只此一个心。枉用于文章。枉用于诗句。枉用于书画。枉用于科场。至今顽然为自暴自弃底人。循省汗出。未知此身。去彼两翼四足而飞走者。为几寸耳。今弟心。正如袯襫家子孙之幼失其父祖所传来许多田地第宅者。却被人诳诱。或远商客方。或寄佣他家。及其年齿之渐大饥寒之日逼然后。还归故里。徊翔踯躅。偶得其残缺文籍于坠弃之中而恍然自悟。始知我初之未尝无田地。又未尝无第宅。却自笑为何而远商客方。为何而寄佣他家。方思持是而访问。返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2H 页
 我田地而耕之。还我第宅而处之。此正穷而反本之谓也。吾兄之于本地。养之有素。利欲之蔽。想不如愚弟之甚。却未知其于不见不闻者。能无屋漏之愧。而凡于应接事物之间。无毫毛人心之间杂者否。吾兄每云人能不作害物事。则自足为善士。此亦可谓自待之太薄而自恕之太宽矣。如桀纣之恶。固已在所不道。未知吾人之责。果可止于不害物而足乎。以不害物而自足。则彼以利物为心者。将非己分事乎。信如兄言。则夫子之铎。不用警于道路矣。邹圣之辙。不用环于天下矣。尧舜不当以不博施济众为病也。文王不必以视民如伤为心也。吾兄何其见仁之小也。如老聃,庄周之学。盖尝不知仁义。而亦不曾身为害物之事。独其载之其书。非圣畔道者。吾儒之所不容。今吾兄虽口不道五千之文,荒唐之说。其自私其身而不以利物益人为心。则未尝不与二氏者同其弊矣。但所谓利物者。非容易事。今若曰存心利物。先自不害物始。循次渐进。以至极致可也。然此亦非谓初用一件心于不害物上着工后。别用一件心于利物上着工也。大抵导吾仁心。推以扩充。应事接物。无少间断。则初觉不害物者为多而利物者为少。后觉利
我田地而耕之。还我第宅而处之。此正穷而反本之谓也。吾兄之于本地。养之有素。利欲之蔽。想不如愚弟之甚。却未知其于不见不闻者。能无屋漏之愧。而凡于应接事物之间。无毫毛人心之间杂者否。吾兄每云人能不作害物事。则自足为善士。此亦可谓自待之太薄而自恕之太宽矣。如桀纣之恶。固已在所不道。未知吾人之责。果可止于不害物而足乎。以不害物而自足。则彼以利物为心者。将非己分事乎。信如兄言。则夫子之铎。不用警于道路矣。邹圣之辙。不用环于天下矣。尧舜不当以不博施济众为病也。文王不必以视民如伤为心也。吾兄何其见仁之小也。如老聃,庄周之学。盖尝不知仁义。而亦不曾身为害物之事。独其载之其书。非圣畔道者。吾儒之所不容。今吾兄虽口不道五千之文,荒唐之说。其自私其身而不以利物益人为心。则未尝不与二氏者同其弊矣。但所谓利物者。非容易事。今若曰存心利物。先自不害物始。循次渐进。以至极致可也。然此亦非谓初用一件心于不害物上着工后。别用一件心于利物上着工也。大抵导吾仁心。推以扩充。应事接物。无少间断。则初觉不害物者为多而利物者为少。后觉利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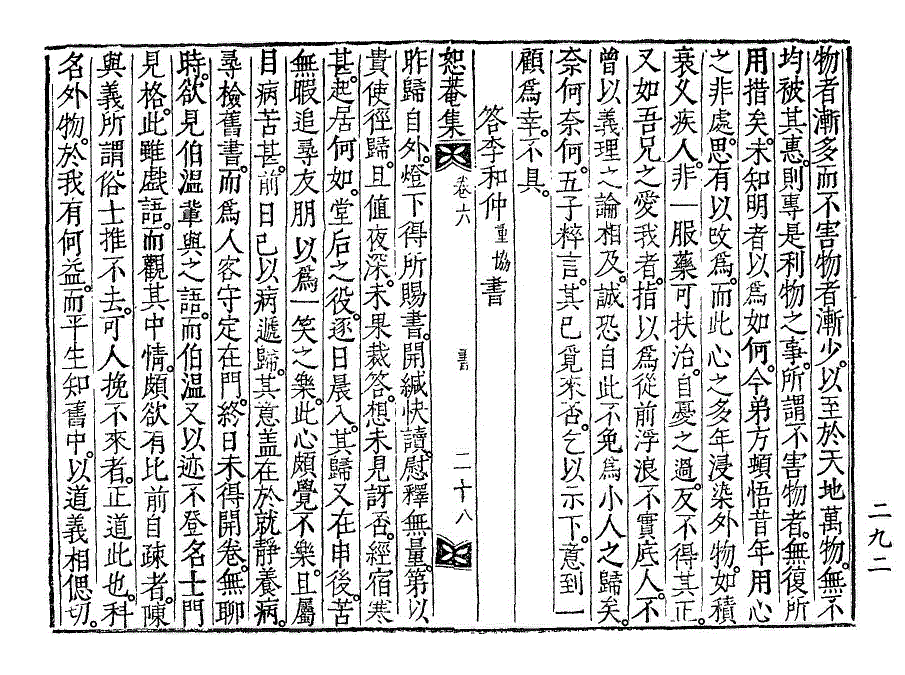 物者渐多而不害物者渐少。以至于天地万物。无不均被其惠。则专是利物之事。所谓不害物者。无复所用措矣。未知明者以为如何。今弟方顿悟昔年用心之非处。思有以改为。而此心之多年浸染外物。如积衰久疾人。非一服药可扶治。自忧之过。反不得其正。又如吾兄之爱我者。指以为从前浮浪不实底人。不曾以义理之论相及。诚恐自此不免为小人之归矣。奈何奈何。五子粹言。其已觅来否。乞以示下。意到一顾为幸。不具。
物者渐多而不害物者渐少。以至于天地万物。无不均被其惠。则专是利物之事。所谓不害物者。无复所用措矣。未知明者以为如何。今弟方顿悟昔年用心之非处。思有以改为。而此心之多年浸染外物。如积衰久疾人。非一服药可扶治。自忧之过。反不得其正。又如吾兄之爱我者。指以为从前浮浪不实底人。不曾以义理之论相及。诚恐自此不免为小人之归矣。奈何奈何。五子粹言。其已觅来否。乞以示下。意到一顾为幸。不具。答李和仲(重协)书
昨归自外。灯下得所赐书。开缄快读。慰释无量。第以贵使径归。且值夜深。未果裁答。想未见讶否。经宿寒甚。起居何如。堂后之役。逐日晨入。其归又在申后。苦无暇追寻友朋以为一笑之乐。此心颇觉不乐。且属目病苦甚。前日已以病递归。其意盖在于就静养病。寻检旧书。而为人客守定在门。终日未得开卷。无聊时。欲见伯温辈与之语。而伯温又以迹不登名士门见格。此虽戏语。而观其中情。颇欲有比前自疏者。陈与义所谓俗士推不去。可人挽不来者。正道此也。科名外物。于我有何益。而平生知旧中。以道义相偲切。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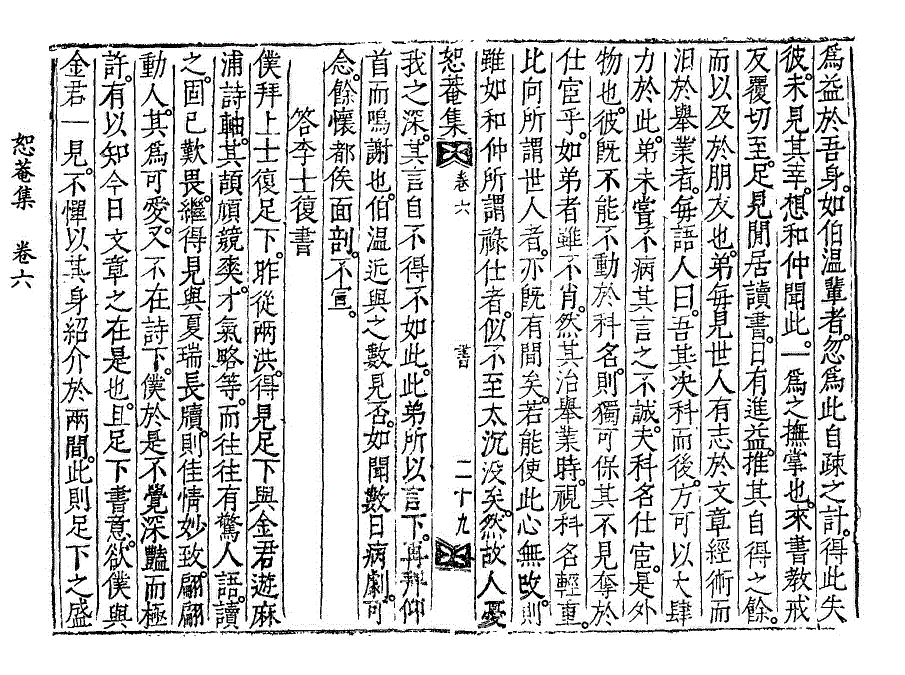 为益于吾身。如伯温辈者。忽为此自疏之计。得此失彼。未见其幸。想和仲闻此。一为之抚掌也。来书教戒反覆切至。足见閒居读书。日有进益。推其自得之馀。而以及于朋友也。弟每见世人有志于文章经术而汨于举业者。每语人曰。吾其决科而后。方可以大肆力于此。弟未尝不病其言之不诚。夫科名仕宦。是外物也。彼既不能不动于科名。则独可保其不见夺于仕宦乎。如弟者虽不肖。然其治举业时。视科名轻重。比向所谓世人者。亦既有间矣。若能使此心无改。则虽如和仲所谓禄仕者。似不至太沉没矣。然故人忧我之深。其言自不得不如此。此弟所以言下。再拜仰首而鸣谢也。伯温近与之数见否。如闻数日病剧。可念。馀怀都俟面剖。不宣。
为益于吾身。如伯温辈者。忽为此自疏之计。得此失彼。未见其幸。想和仲闻此。一为之抚掌也。来书教戒反覆切至。足见閒居读书。日有进益。推其自得之馀。而以及于朋友也。弟每见世人有志于文章经术而汨于举业者。每语人曰。吾其决科而后。方可以大肆力于此。弟未尝不病其言之不诚。夫科名仕宦。是外物也。彼既不能不动于科名。则独可保其不见夺于仕宦乎。如弟者虽不肖。然其治举业时。视科名轻重。比向所谓世人者。亦既有间矣。若能使此心无改。则虽如和仲所谓禄仕者。似不至太沉没矣。然故人忧我之深。其言自不得不如此。此弟所以言下。再拜仰首而鸣谢也。伯温近与之数见否。如闻数日病剧。可念。馀怀都俟面剖。不宣。答李士复书
仆拜上士复足下。昨从两洪。得见足下与金君游麻浦诗轴。其颉颃竞爽。才气略等。而往往有惊人语。读之。固已叹畏。继得见与夏瑞长牍。则佳情妙致。翩翩动人。其为可爱。又不在诗下。仆于是不觉深艳而极许。有以知今日文章之在是也。且足下书意。欲仆与金君一见。不惮以其身绍介于两间。此则足下之盛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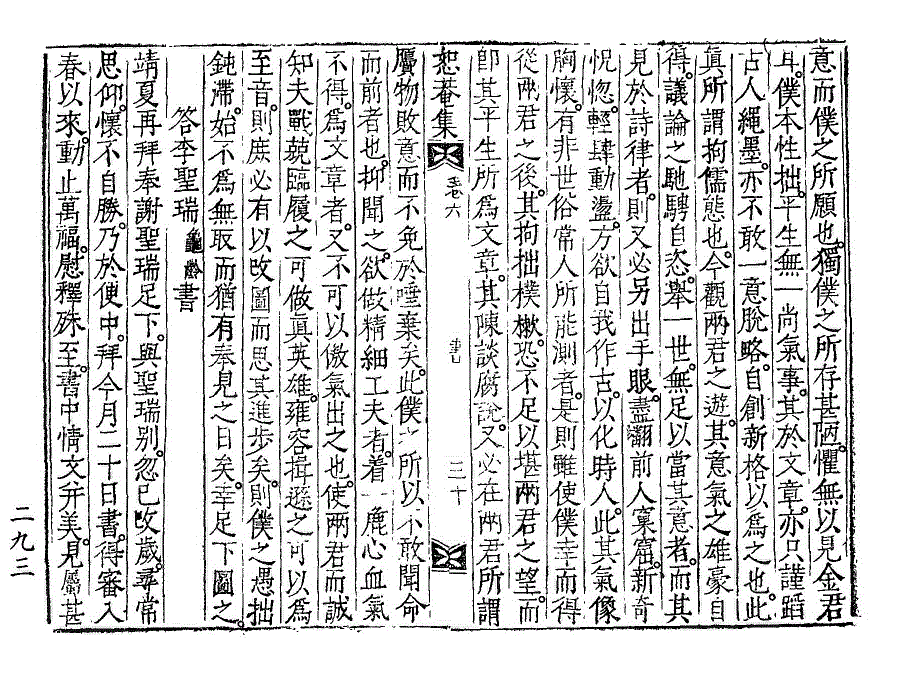 意而仆之所愿也。独仆之所存甚陋。惧无以见金君耳。仆本性拙。平生无一尚气事。其于文章。亦只谨蹈古人绳墨。亦不敢一意脱略。自创新格以为之也。此真所谓拘儒态也。今观两君之游。其意气之雄豪自得。议论之驰骋自恣。举一世。无足以当其意者。而其见于诗律者。则又必另出手眼。尽翻前人窠窟。新奇恍惚。轻肆动荡。方欲自我作古。以化时人。此其气像胸怀。有非世俗常人所能测者。是则虽使仆幸而得从两君之后。其拘拙朴樕。恐不足以堪两君之望。而即其平生所为文章。其陈谈腐说。又必在两君所谓赝物败意而不免于唾弃矣。此仆之所以不敢闻命而前者也。抑闻之。欲做精细工夫者。着一粗心血气不得。为文章者。又不可以傲气出之也。使两君而诚知夫战兢临履之可做真英雄。雍容揖逊之可以为至音。则庶必有以改图而思其进步矣。则仆之愚拙钝滞。始不为无取而犹有奉见之日矣。幸足下图之。
意而仆之所愿也。独仆之所存甚陋。惧无以见金君耳。仆本性拙。平生无一尚气事。其于文章。亦只谨蹈古人绳墨。亦不敢一意脱略。自创新格以为之也。此真所谓拘儒态也。今观两君之游。其意气之雄豪自得。议论之驰骋自恣。举一世。无足以当其意者。而其见于诗律者。则又必另出手眼。尽翻前人窠窟。新奇恍惚。轻肆动荡。方欲自我作古。以化时人。此其气像胸怀。有非世俗常人所能测者。是则虽使仆幸而得从两君之后。其拘拙朴樕。恐不足以堪两君之望。而即其平生所为文章。其陈谈腐说。又必在两君所谓赝物败意而不免于唾弃矣。此仆之所以不敢闻命而前者也。抑闻之。欲做精细工夫者。着一粗心血气不得。为文章者。又不可以傲气出之也。使两君而诚知夫战兢临履之可做真英雄。雍容揖逊之可以为至音。则庶必有以改图而思其进步矣。则仆之愚拙钝滞。始不为无取而犹有奉见之日矣。幸足下图之。答李圣瑞(龟龄)书
靖夏再拜奉谢圣瑞足下。与圣瑞别。忽已改岁。寻常思仰。怀不自胜。乃于便中。拜今月二十日书。得审入春以来。动止万福。慰释殊至。书中情文并美。见属甚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4H 页
 厚。自惟以弟不肖。何以得此于圣瑞。仆之从圣瑞游几半载。自谓尽知圣瑞所存。曾未敢遽谓其文辞之外。又能有高见明识。今者来示。乃能如此。然则向之所以知圣瑞于半载者。乃反为浅。而今之得之于一书者为多。三复感叹。不知所以为谢也。示百家文。虽非急务。亦不可不一看。如战策之浑雄。左国之雅洁。孙吴之谋。申韩之辩。各自有可观。而至如荀卿。乃其立言论道。帅战国以来一人。故其文比向者数子。颇醇实。使后之学者。能不病于其性恶之说。而只取其言之最醇者。则不为无益。恐不可全弃。如唐宋八君子之文。或出于传记。或出于子史。或有并取老庄禅宗之旨者。各自名家。虽其取舍不同。醇漓有间。而要之为文之圣则一也。其中如退之之卓然自立。以吾道为己任者。尤为难得。而其他数子。亦皆一代伟人。当时莫不以经纶事业自期。其平生议论见识。互见于所论著。岂皆为空言无实之归哉。来书又云欲读朱书甚善。其为书千端万绪。说尽道理。仁思义色。相济表里。浩浩如江水之方生。而其可喜处。正在于明白洞快。自有天地以来。未曾有如许大文字。士之有志于斯文者。诚不可不读。要之八家之文。以意行文。
厚。自惟以弟不肖。何以得此于圣瑞。仆之从圣瑞游几半载。自谓尽知圣瑞所存。曾未敢遽谓其文辞之外。又能有高见明识。今者来示。乃能如此。然则向之所以知圣瑞于半载者。乃反为浅。而今之得之于一书者为多。三复感叹。不知所以为谢也。示百家文。虽非急务。亦不可不一看。如战策之浑雄。左国之雅洁。孙吴之谋。申韩之辩。各自有可观。而至如荀卿。乃其立言论道。帅战国以来一人。故其文比向者数子。颇醇实。使后之学者。能不病于其性恶之说。而只取其言之最醇者。则不为无益。恐不可全弃。如唐宋八君子之文。或出于传记。或出于子史。或有并取老庄禅宗之旨者。各自名家。虽其取舍不同。醇漓有间。而要之为文之圣则一也。其中如退之之卓然自立。以吾道为己任者。尤为难得。而其他数子。亦皆一代伟人。当时莫不以经纶事业自期。其平生议论见识。互见于所论著。岂皆为空言无实之归哉。来书又云欲读朱书甚善。其为书千端万绪。说尽道理。仁思义色。相济表里。浩浩如江水之方生。而其可喜处。正在于明白洞快。自有天地以来。未曾有如许大文字。士之有志于斯文者。诚不可不读。要之八家之文。以意行文。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4L 页
 故意奇而文亦高。考亭之书。以理为文。故理尽而文亦达。 皇明诸子之文。以文生意。故语无归趣而文无可观。世之为文者。诚能以 皇明诸子为戒。始取裁于八家而终归宿于考亭。则文之道于斯尽矣。足下见识深到。其于为文之道。必不待仆言而得之。但来书欲使仆有言。故有不敢自外尔。且圣瑞以无强辅为忧。夫师友之为益于人。岂浅鲜哉。毋论问学文章。俱不可一日亏阙。而然而在我必先有自得之妙。然后在彼方有发药之道。若使我无自得乎中。亦必无自信者矣。既不能自信。则又将不信人矣。然则彼虽有言。我将何所据而取舍哉。今圣瑞之志。固未易得。而其于自得之妙。犹有所未尽者。仆以为圣瑞必更着工于此然后。方可以望人之益我也。未知如何。离别已久。怀思渐恶。追想旧游。或为之怅然移日。忽得来书。恍接别来面目。为慰不少。愿圣瑞有以继之也。人还匆匆。草谢不具。
故意奇而文亦高。考亭之书。以理为文。故理尽而文亦达。 皇明诸子之文。以文生意。故语无归趣而文无可观。世之为文者。诚能以 皇明诸子为戒。始取裁于八家而终归宿于考亭。则文之道于斯尽矣。足下见识深到。其于为文之道。必不待仆言而得之。但来书欲使仆有言。故有不敢自外尔。且圣瑞以无强辅为忧。夫师友之为益于人。岂浅鲜哉。毋论问学文章。俱不可一日亏阙。而然而在我必先有自得之妙。然后在彼方有发药之道。若使我无自得乎中。亦必无自信者矣。既不能自信。则又将不信人矣。然则彼虽有言。我将何所据而取舍哉。今圣瑞之志。固未易得。而其于自得之妙。犹有所未尽者。仆以为圣瑞必更着工于此然后。方可以望人之益我也。未知如何。离别已久。怀思渐恶。追想旧游。或为之怅然移日。忽得来书。恍接别来面目。为慰不少。愿圣瑞有以继之也。人还匆匆。草谢不具。答柳垂甫(绅)弟书
向足下赐仆书累百言。观其旨意。盖以科举禄利为倘来之物。而问学文章为自己之责。不可弃自己之所切急而事倘来之不可必。若翻然深悔于既往而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5H 页
 欲自勉懋于来者。此盖足下善心之发。而其勇决。殆仆之所不及。善哉善哉。虽然仆欲有问于足下者。足下之所谓爱慕古人问学文章者。其心诚好之。如其言耶。抑出于一时之愤发而不知其言之遂至此乎。此仆之所不能无疑也。彼所谓科举之文者。亦不可以易言也。其业之轻重。固不可与问学文章比论。然其所以耗心劳精。搯肾擢胃。脱去陈腐而入于新奇者。非捐一二十年之勤。固不可以决其得失也。仆幼时偶见不以此勤而得者。遂妄以为科举甚易。遂尽力于古人文章而时出其馀。以应有司之选。不知夫向得者之有幸焉。又不知其幸得之不为贵也。数年以来。愈数不利于场屋。及至今日而无有所得。则颇已知其难矣。既知其难。则应有以改向之所为矣。然知其难而犹不以改之者。盖吾心之所轻重于彼此者存焉尔。今足下无仆之甚困而早知其难则可谓幸矣。然今足下之言。仆不觉欣然喜之。而卒不能不使仆忧之。盖喜之者。喜此心之将发也。忧之者。忧此心之难继也。今足下果能坚持此心。决然谢去科举之累。闭门屈首。驰骋百家。日有以自乐。则必其胸中所得。难以猎一科沾一禄。以占一身之荣利而忽焉
欲自勉懋于来者。此盖足下善心之发。而其勇决。殆仆之所不及。善哉善哉。虽然仆欲有问于足下者。足下之所谓爱慕古人问学文章者。其心诚好之。如其言耶。抑出于一时之愤发而不知其言之遂至此乎。此仆之所不能无疑也。彼所谓科举之文者。亦不可以易言也。其业之轻重。固不可与问学文章比论。然其所以耗心劳精。搯肾擢胃。脱去陈腐而入于新奇者。非捐一二十年之勤。固不可以决其得失也。仆幼时偶见不以此勤而得者。遂妄以为科举甚易。遂尽力于古人文章而时出其馀。以应有司之选。不知夫向得者之有幸焉。又不知其幸得之不为贵也。数年以来。愈数不利于场屋。及至今日而无有所得。则颇已知其难矣。既知其难。则应有以改向之所为矣。然知其难而犹不以改之者。盖吾心之所轻重于彼此者存焉尔。今足下无仆之甚困而早知其难则可谓幸矣。然今足下之言。仆不觉欣然喜之。而卒不能不使仆忧之。盖喜之者。喜此心之将发也。忧之者。忧此心之难继也。今足下果能坚持此心。决然谢去科举之累。闭门屈首。驰骋百家。日有以自乐。则必其胸中所得。难以猎一科沾一禄。以占一身之荣利而忽焉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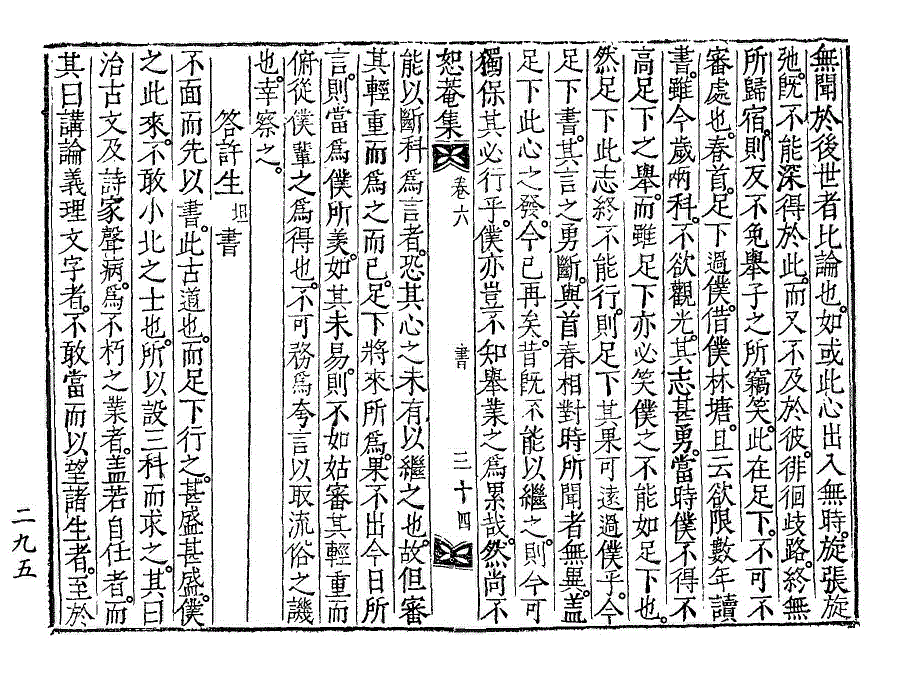 无闻于后世者比论也。如或此心出入无时。旋张旋弛。既不能深得于此。而又不及于彼。徘徊歧路。终无所归宿。则反不免举子之所窃笑。此在足下。不可不审处也。春首。足下过仆。借仆林塘。且云欲限数年读书。虽今岁两科。不欲观光。其志甚勇。当时仆不得不高足下之举。而虽足下亦必笑仆之不能如足下也。然足下此志终不能行。则足下其果可远过仆乎。今足下书。其言之勇断。与首春相对时所闻者无异。盖足下此心之发。今已再矣。昔既不能以继之。则今可独保其必行乎。仆亦岂不知举业之为累哉。然尚不能以断科为言者。恐其心之未有以继之也。故但审其轻重而为之而已。足下将来所为。果不出今日所言。则当为仆所羡。如其未易。则不如姑审其轻重而俯从仆辈之为得也。不可务为夸言以取流俗之讥也。幸察之。
无闻于后世者比论也。如或此心出入无时。旋张旋弛。既不能深得于此。而又不及于彼。徘徊歧路。终无所归宿。则反不免举子之所窃笑。此在足下。不可不审处也。春首。足下过仆。借仆林塘。且云欲限数年读书。虽今岁两科。不欲观光。其志甚勇。当时仆不得不高足下之举。而虽足下亦必笑仆之不能如足下也。然足下此志终不能行。则足下其果可远过仆乎。今足下书。其言之勇断。与首春相对时所闻者无异。盖足下此心之发。今已再矣。昔既不能以继之。则今可独保其必行乎。仆亦岂不知举业之为累哉。然尚不能以断科为言者。恐其心之未有以继之也。故但审其轻重而为之而已。足下将来所为。果不出今日所言。则当为仆所羡。如其未易。则不如姑审其轻重而俯从仆辈之为得也。不可务为夸言以取流俗之讥也。幸察之。答许生(坦)书
不面而先以书。此古道也。而足下行之。甚盛甚盛。仆之此来。不敢小北之士也。所以设三科而求之。其曰治古文及诗家声病。为不朽之业者。盖若自任者。而其曰讲论义理文字者。不敢当而以望诸生者。至于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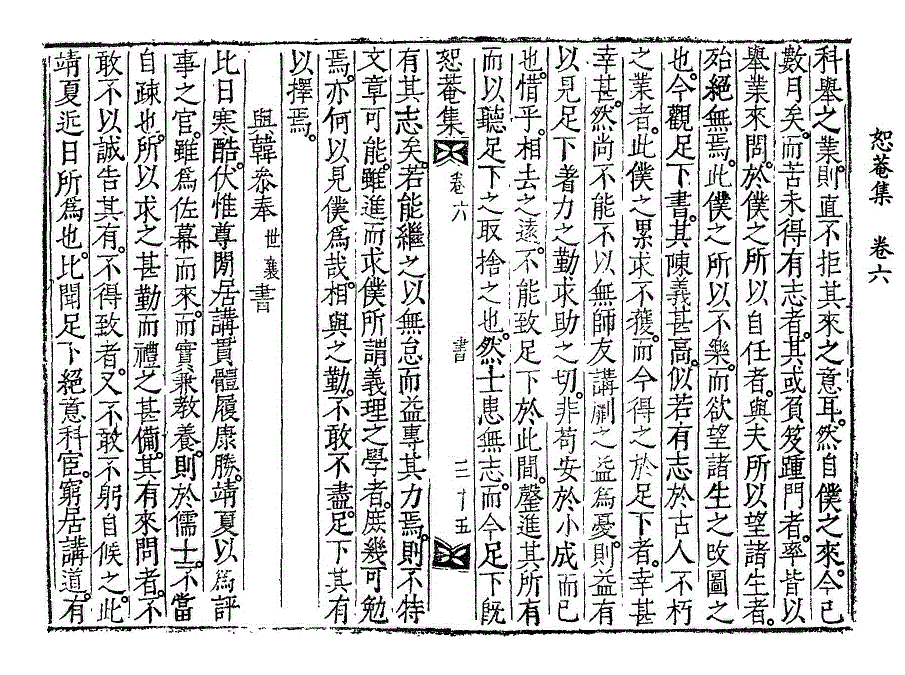 科举之业。则直不拒其来之意耳。然自仆之来。今已数月矣。而苦未得有志者。其或负笈踵门者。率皆以举业来问。于仆之所以自任者。与夫所以望诸生者。殆绝无焉。此仆之所以不乐。而欲望诸生之改图之也。今观足下书。其陈义甚高。似若有志于古人不朽之业者。此仆之累求不获。而今得之于足下者。幸甚幸甚。然尚不能不以无师友讲劘之益为忧。则益有以见足下着力之勤求助之切。非苟安于小成而已也。惜乎。相去之远。不能致足下于此间。罄进其所有而以听足下之取舍之也。然士患无志。而今足下既有其志矣。若能继之以无怠而益专其力焉。则不特文章可能。虽进而求仆所谓义理之学者。庶几可勉焉。亦何以见仆为哉。相与之勤。不敢不尽。足下其有以择焉。
科举之业。则直不拒其来之意耳。然自仆之来。今已数月矣。而苦未得有志者。其或负笈踵门者。率皆以举业来问。于仆之所以自任者。与夫所以望诸生者。殆绝无焉。此仆之所以不乐。而欲望诸生之改图之也。今观足下书。其陈义甚高。似若有志于古人不朽之业者。此仆之累求不获。而今得之于足下者。幸甚幸甚。然尚不能不以无师友讲劘之益为忧。则益有以见足下着力之勤求助之切。非苟安于小成而已也。惜乎。相去之远。不能致足下于此间。罄进其所有而以听足下之取舍之也。然士患无志。而今足下既有其志矣。若能继之以无怠而益专其力焉。则不特文章可能。虽进而求仆所谓义理之学者。庶几可勉焉。亦何以见仆为哉。相与之勤。不敢不尽。足下其有以择焉。与韩参奉(世襄)书
比日寒酷。伏惟尊閒居讲贯体履康胜。靖夏以为评事之官。虽为佐幕而来。而实兼教养。则于儒士。不当自疏也。所以求之甚勤而礼之甚备。其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告其有。不得致者。又不敢不躬自候之。此靖夏近日所为也。比闻足下绝意科宦。穷居讲道。有
恕庵集卷之六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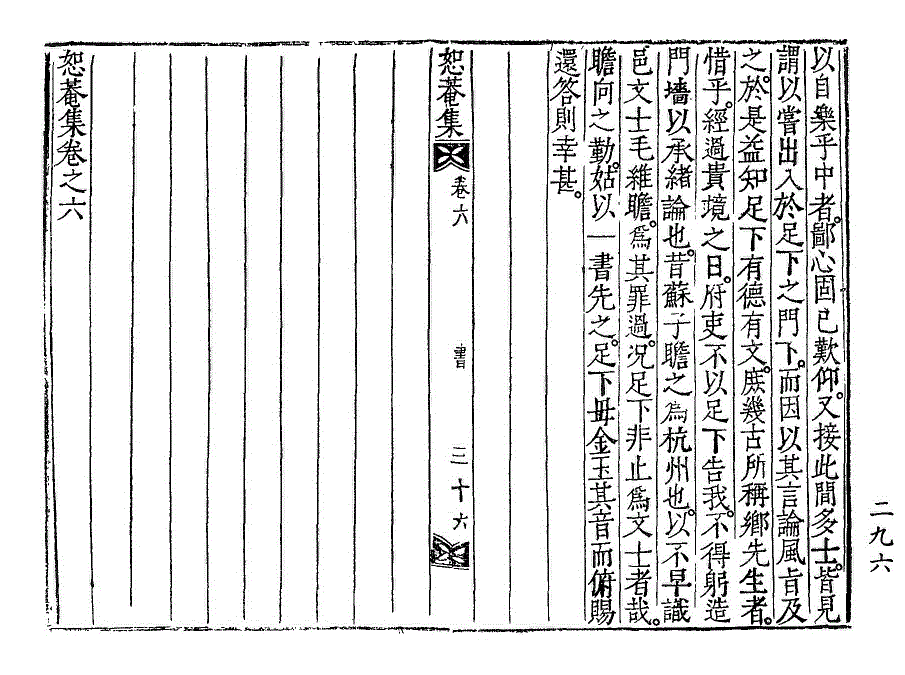 以自乐乎中者。鄙心固已叹仰。又接此间多士。皆见谓以尝出入于足下之门下。而因以其言论风旨及之。于是益知足下有德有文。庶几古所称乡先生者。惜乎。经过贵境之日。府吏不以足下告我。不得躬造门墙以承绪论也。昔苏子瞻之为杭州也。以不早识邑文士毛维瞻。为其罪过。况足下非止为文士者哉。瞻向之勤。姑以一书先之。足下毋金玉其音而俯赐还答则幸甚。
以自乐乎中者。鄙心固已叹仰。又接此间多士。皆见谓以尝出入于足下之门下。而因以其言论风旨及之。于是益知足下有德有文。庶几古所称乡先生者。惜乎。经过贵境之日。府吏不以足下告我。不得躬造门墙以承绪论也。昔苏子瞻之为杭州也。以不早识邑文士毛维瞻。为其罪过。况足下非止为文士者哉。瞻向之勤。姑以一书先之。足下毋金玉其音而俯赐还答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