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下集卷之十 第 x 页
白下集卷之十
序
序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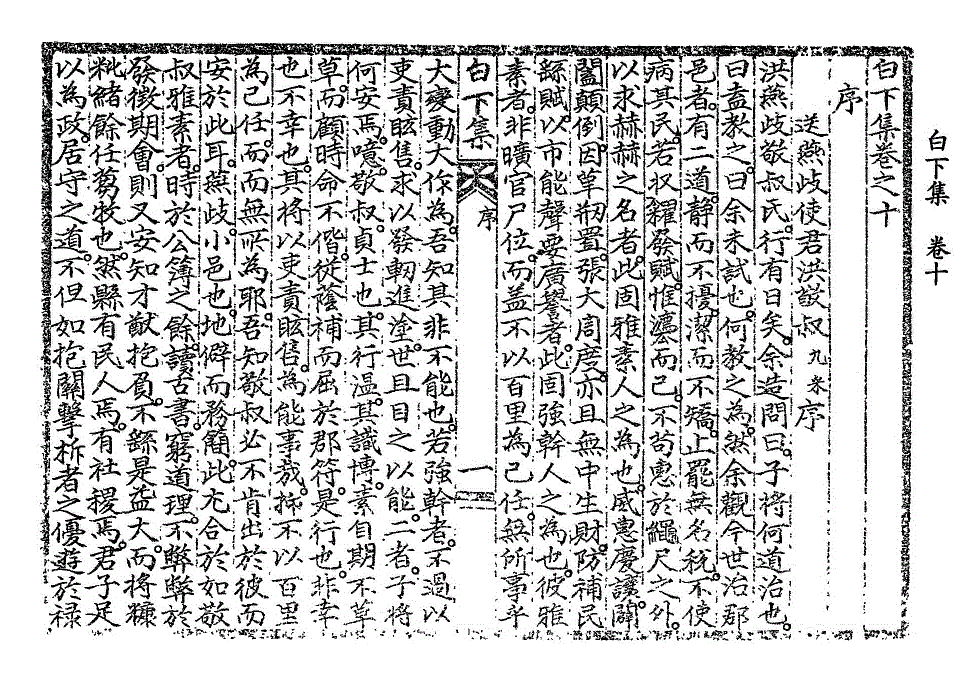 送燕歧使君洪敬叔(九采)序
送燕歧使君洪敬叔(九采)序洪燕歧敬叔氏。行有日矣。余造问曰。子将何道治也。曰盍教之。曰余未试也。何教之为。然余观今世治郡邑者。有二道。静而不扰。洁而不矫。止罢无名税。不使病其民。若收籴发赋。惟法而已。不苟惠于绳尺之外。以求赫赫之名者。此固雅素人之为也。威惠庆让。辟阖颠倒。因革刱置。张大周度。亦且无中生财。防补民繇赋。以市能声要广誉者。此固强干人之为也。彼雅素者。非旷官尸位。而盖不以百里为己任。无所事乎大变动大作为。吾知其非不能也。若强干者。不过以吏责眩售。求以发轫进涂。世且目之以能。二者。子将何安焉。噫。敬叔。贞士也。其行温。其识博。素自期不草草。而顾时命不偕。从荫补而屈于郡符。是行也。非幸也不幸也。其将以吏责眩售。为能事哉。抑不以百里为己任。而而无所为耶。吾知敬叔必不肯出于彼而安于此耳。燕歧。小邑也。地僻而务简。此尤合于如敬叔雅素者。时于公簿之馀。读古书。穷道理。不弊弊于发徵期会。则又安知才猷抱负。不繇是益大。而将糠秕绪馀任刍牧也。然县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君子足以为政。居守之道。不但如抱关击柝者之优游于禄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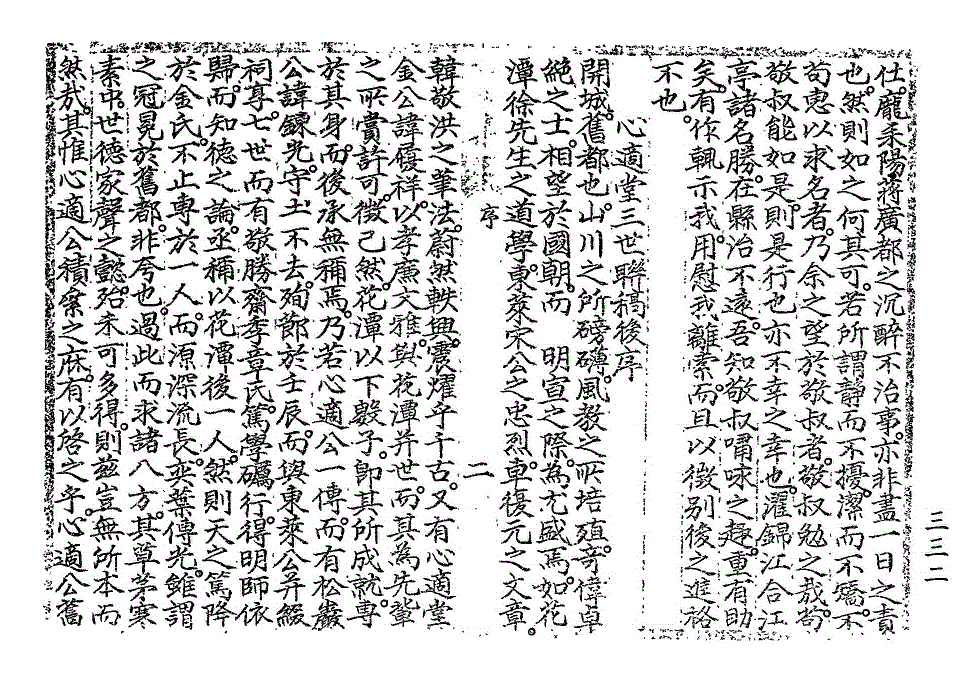 仕。庞耒阳,蒋广都之沉醉不治事。亦非尽一日之责也。然则如之何其可。若所谓静而不扰。洁而不矫。不苟惠以求名者。乃余之望于敬叔者。敬叔勉之哉。苟敬叔能如是。则是行也亦不幸之幸也。濯锦江合江亭诸名胜。在县治不远。吾知敬叔啸咏之趣。重有助矣。有作辄示我。用慰我离索。而且以徵别后之进格不也。
仕。庞耒阳,蒋广都之沉醉不治事。亦非尽一日之责也。然则如之何其可。若所谓静而不扰。洁而不矫。不苟惠以求名者。乃余之望于敬叔者。敬叔勉之哉。苟敬叔能如是。则是行也亦不幸之幸也。濯锦江合江亭诸名胜。在县治不远。吾知敬叔啸咏之趣。重有助矣。有作辄示我。用慰我离索。而且以徵别后之进格不也。心适堂三世联稿后序
开城。旧都也。山川之所磅礴。风教之所培殖。奇伟卓绝之士。相望于国朝。而 明宣之际。为尤盛焉。如花潭徐先生之道学。东莱宋公之忠烈。车复元之文章。韩敬洪之笔法。蔚然轶兴。震耀乎千古。又有心适堂金公讳履祥。以孝廉文雅。与花潭并世。而其为先辈之所赏许。可徵已。然花潭以下数子。即其所成就。专于其身。而后承无称焉。乃若心适公一传。而有松岩公讳鍊光。守土不去。殉节于壬辰。而与东莱公并缀祠享。七世而有敬胜斋季章氏。笃学砺行。得明师依归。而知德之论。亟称以花潭后一人。然则天之笃降于金氏。不止专于一人。而源深流长。奕叶传光。虽谓之冠冕于旧都。非夸也。过此而求诸八方。其草茅寒素中。世德家声之懿。殆未可多得。则玆岂无所本而然哉。其惟心适公积累之庥。有以启之乎。心适公旧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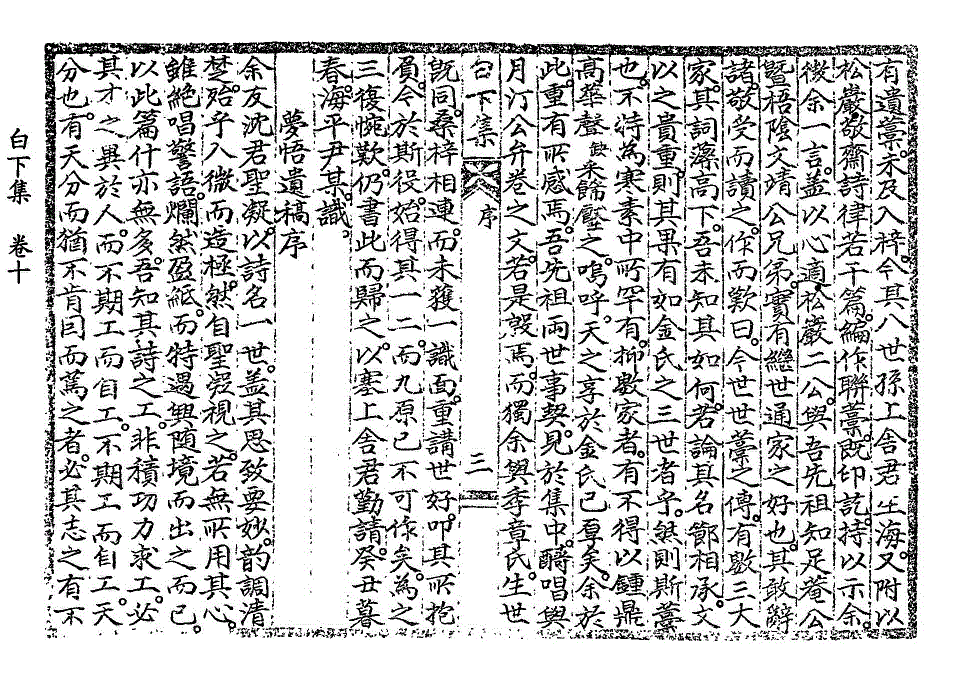 有遗藁。未及入梓。今其八世孙上舍君生海。又附以松岩,敬斋诗律若干篇。编作联藁。既印讫。持以示余。徵余一言。盖以心适,松岩二公。与吾先祖知足庵公暨梧阴文靖公兄弟。实有继世通家之好也。其敢辞诸。敬受而读之。作而叹曰。今世世藁之传。有数三大家。其词藻高下。吾未知其如何。若论其名节相承。文以之贵重。则其果有如金氏之三世者乎。然则斯藁也。不特为寒素中所罕有。抑数家者。有不得以钟鼎高华声(缺)采饰压之。呜呼。天之享于金氏已厚矣。余于此。重有所感焉。吾先祖两世事契。见于集中。酬唱与月汀公弁卷之文。若是殷焉。而独余与季章氏。生世既同。桑梓相连。而未获一识面。重讲世好。叩其所抱负。今于斯役。始得其一二。而九原已不可作矣。为之三复惋叹。仍书此而归之。以塞上舍君勤请。癸丑暮春。海平尹某。识。
有遗藁。未及入梓。今其八世孙上舍君生海。又附以松岩,敬斋诗律若干篇。编作联藁。既印讫。持以示余。徵余一言。盖以心适,松岩二公。与吾先祖知足庵公暨梧阴文靖公兄弟。实有继世通家之好也。其敢辞诸。敬受而读之。作而叹曰。今世世藁之传。有数三大家。其词藻高下。吾未知其如何。若论其名节相承。文以之贵重。则其果有如金氏之三世者乎。然则斯藁也。不特为寒素中所罕有。抑数家者。有不得以钟鼎高华声(缺)采饰压之。呜呼。天之享于金氏已厚矣。余于此。重有所感焉。吾先祖两世事契。见于集中。酬唱与月汀公弁卷之文。若是殷焉。而独余与季章氏。生世既同。桑梓相连。而未获一识面。重讲世好。叩其所抱负。今于斯役。始得其一二。而九原已不可作矣。为之三复惋叹。仍书此而归之。以塞上舍君勤请。癸丑暮春。海平尹某。识。梦悟遗稿序
余友沈君圣凝。以诗名一世。盖其思致要妙。韵调清楚。殆乎入微而造极。然自圣凝视之。若无所用其心。虽绝唱警语。烂然盈纸。而特遇兴随境而出之而已。以此篇什亦无多。吾知其诗之工。非积功力求工。必其才之异于人。而不期工而自工。不期工而自工。天分也。有天分而犹不肯因而笃之者。必其志之有不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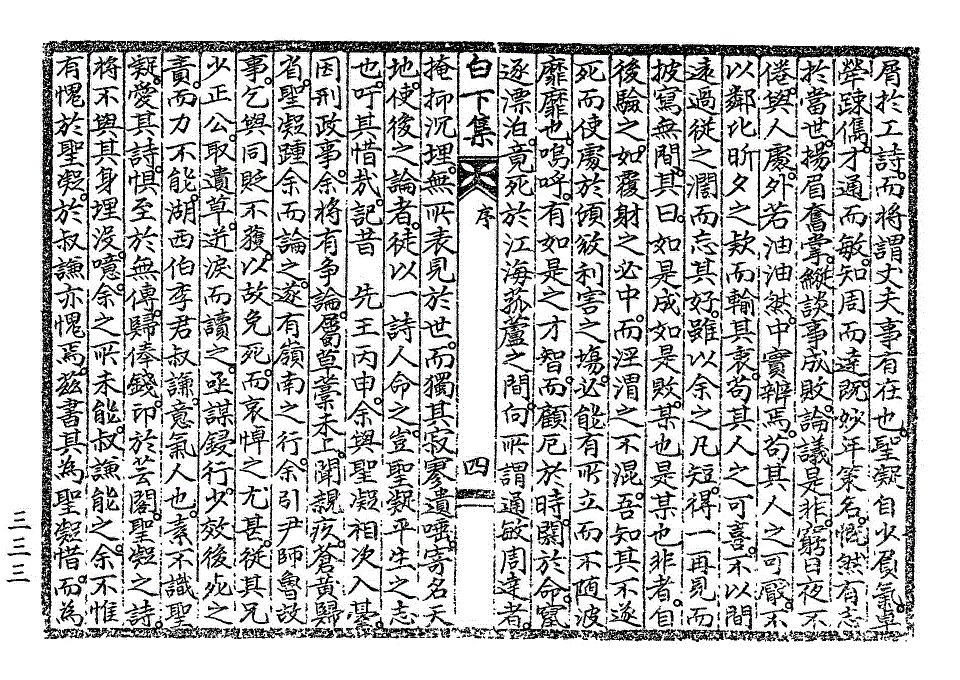 屑于工诗。而将谓丈夫事有在也。圣凝自少负气。卓荦疏俊。才通而敏。知周而达。既妙年策名。慨然有志于当世。扬眉奋掌。纵谈事成败。论议是非。穷日夜不倦。与人处。外若油油然。中实辨焉。苟其人之可厌。不以邻比昕夕之款而输其衷。苟其人之可喜。不以间远过从之阔而忘其好。虽以余之凡短。得一再见而披写无间。其曰。如是成如是败。某也是某也非者。自后验之。如覆射之必中。而泾渭之不混。吾知其不遂死而使处于倾敚利害之场。必能有所立而不随波靡靡也。呜呼。有如是之才智。而顾厄于时。阏于命。窜逐漂泊。竟死于江海菰芦之间。向所谓通敏周达者。掩抑沉埋。无所表见于世。而独其寂寥遗唾。寄名天地。使后之论者。徒以一诗人命之。岂圣凝平生之志也。吁其惜哉。记昔 先王丙申。余与圣凝相次入台。因刑政事。余将有争论。属草藁未上。闻亲疚。苍黄归省。圣凝踵余而论之。遂有岭南之行。余引尹师鲁故事。乞与同贬不获。以故免死。而哀悼之尤甚。从其兄少正公。取遗草。迸泪而读之。亟谋锓行。少效后死之责。而力不能。湖西伯李君叔谦。意气人也。素不识圣凝。爱其诗。惧至于无传。归俸钱。印于芸阁。圣凝之诗。将不与其身埋没。噫。余之所未能。叔谦能之。余不惟有愧于圣凝。于叔谦亦愧焉。玆书其为圣凝惜。而为
屑于工诗。而将谓丈夫事有在也。圣凝自少负气。卓荦疏俊。才通而敏。知周而达。既妙年策名。慨然有志于当世。扬眉奋掌。纵谈事成败。论议是非。穷日夜不倦。与人处。外若油油然。中实辨焉。苟其人之可厌。不以邻比昕夕之款而输其衷。苟其人之可喜。不以间远过从之阔而忘其好。虽以余之凡短。得一再见而披写无间。其曰。如是成如是败。某也是某也非者。自后验之。如覆射之必中。而泾渭之不混。吾知其不遂死而使处于倾敚利害之场。必能有所立而不随波靡靡也。呜呼。有如是之才智。而顾厄于时。阏于命。窜逐漂泊。竟死于江海菰芦之间。向所谓通敏周达者。掩抑沉埋。无所表见于世。而独其寂寥遗唾。寄名天地。使后之论者。徒以一诗人命之。岂圣凝平生之志也。吁其惜哉。记昔 先王丙申。余与圣凝相次入台。因刑政事。余将有争论。属草藁未上。闻亲疚。苍黄归省。圣凝踵余而论之。遂有岭南之行。余引尹师鲁故事。乞与同贬不获。以故免死。而哀悼之尤甚。从其兄少正公。取遗草。迸泪而读之。亟谋锓行。少效后死之责。而力不能。湖西伯李君叔谦。意气人也。素不识圣凝。爱其诗。惧至于无传。归俸钱。印于芸阁。圣凝之诗。将不与其身埋没。噫。余之所未能。叔谦能之。余不惟有愧于圣凝。于叔谦亦愧焉。玆书其为圣凝惜。而为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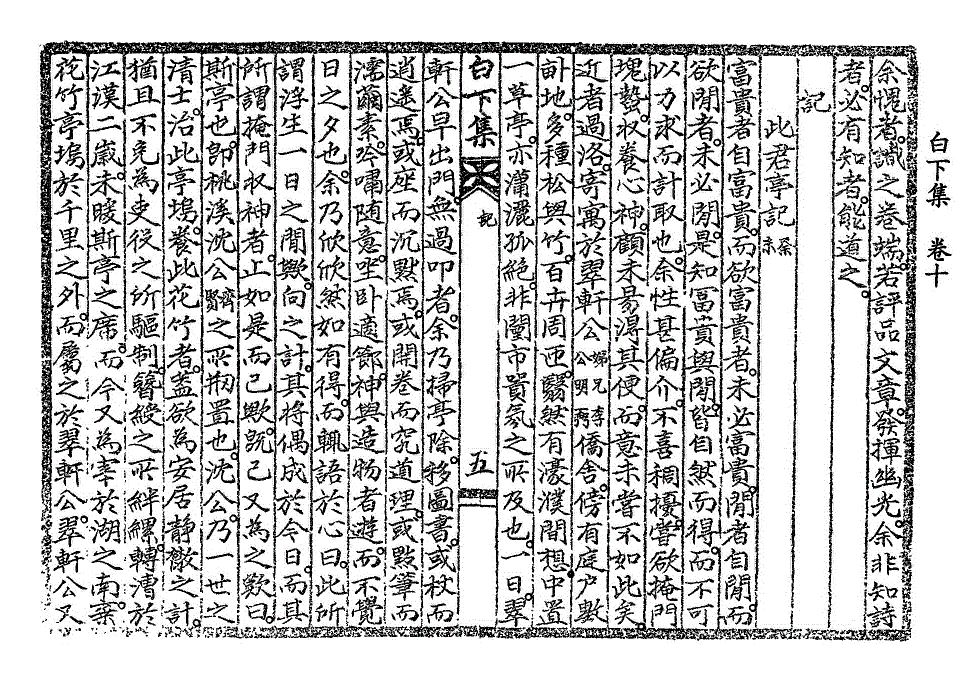 余愧者。识之卷端。若评品文章。发挥幽光。余非知诗者。必有知者。能道之。
余愧者。识之卷端。若评品文章。发挥幽光。余非知诗者。必有知者。能道之。白下集卷之十
记
此君亭记(癸未)
富贵者自富贵。而欲富贵者。未必富贵。閒者自閒。而欲閒者。未必閒。是知富贵与閒。皆自然而得。而不可以力求而计取也。余性甚偏介。不喜稠扰。尝欲掩门块蛰。收养心神。顾未易得其便。而意未尝不如此矣。近者过洛。寄寓于翠轩公(娣兄李公明弼)侨舍。傍有庭户数𤱈地。多种松与竹。百卉周匝。翳然有濠濮间想。中置一草亭。亦潇洒孤绝。非闉市嚣氛之所及也。一日。翠轩公早出门。无过叩者。余乃扫亭除。移图书。或杖而逍遥焉。或座而沉默焉。或开卷而究道理。或点笔而濡茧素。吟啸随意。坐卧适节。神与造物者游。而不觉日之夕也。余乃欣欣然如有得。而辄语于心曰。此所谓浮生一日之閒欤。向之计。其将偶成于今日。而其所谓掩门收神者。止如是而已欤。既已又为之叹曰。斯亭也。即桃溪沈公(齐贤)之所刱置也。沈公。乃一世之清士。治此亭坞。养此花竹者。盖欲为安居静散之计。犹且不免为吏役之所驱制。簪绶之所绊缧。转漕于江汉二岁。未暖斯亭之席。而今又为宰于湖之南。弃花竹亭坞于千里之外。而属之于翠轩公。翠轩公又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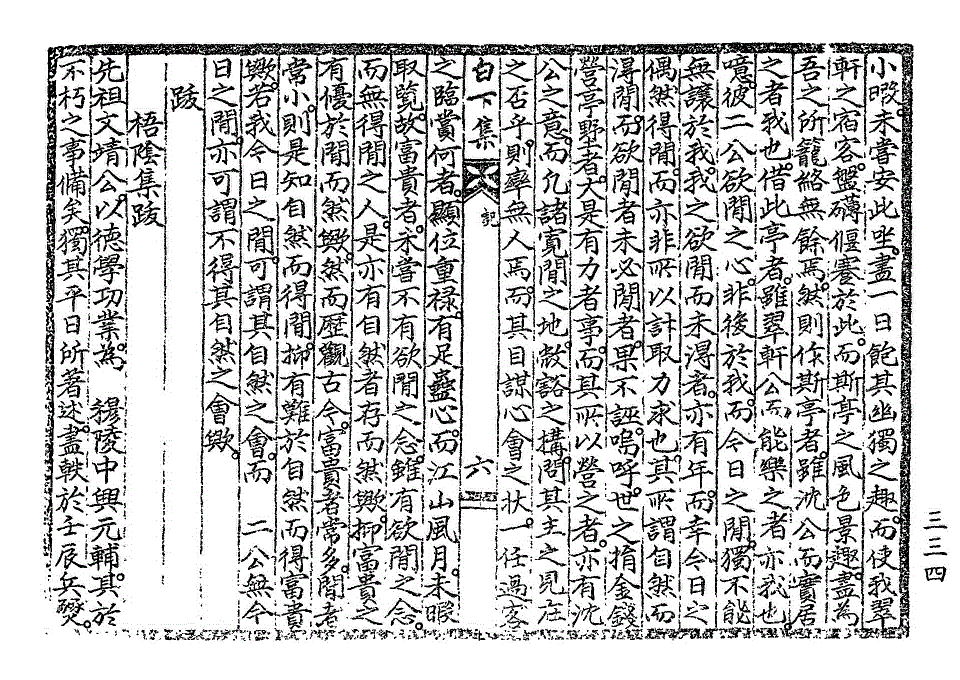 小暇。未尝安此坐。尽一日饱其幽独之趣。而使我翠轩之宿客。盘礴偃蹇于此。而斯亭之风色景趣。尽为吾之所笼络无馀焉。然则作斯亭者。虽沈公而实居之者我也。借此亭者。虽翠轩公而能乐之者亦我也。噫。彼二公欲閒之心。非后于我。而今日之閒。独不能无让于我。我之欲閒而未得者。亦有年。而幸今日之偶然得閒。而亦非所以计取力求也。其所谓自然而得閒。而欲閒者未必閒者。果不诬。呜呼。世之捐金钱营亭墅者。大是有力者事。而其所以营之者。亦有沈公之意。而凡诸宽閒之地。敞豁之搆。问其主之见在之否乎。则率无人焉。而其目谋心会之状。一任过客之临赏何者。显位重禄。有足蛊心。而江山风月。未暇取览。故富贵者。未尝不有欲閒之念。虽有欲閒之念。而无得閒之人。是亦有自然者存而然欤。抑富贵之有优于閒而然欤。然而历观古今。富贵者常多。閒者常小。则是知自然而得閒。抑有难于自然而得富贵欤。若我今日之閒。可谓其自然之会。而 二公无今日之閒。亦可谓不得其自然之会欤。
小暇。未尝安此坐。尽一日饱其幽独之趣。而使我翠轩之宿客。盘礴偃蹇于此。而斯亭之风色景趣。尽为吾之所笼络无馀焉。然则作斯亭者。虽沈公而实居之者我也。借此亭者。虽翠轩公而能乐之者亦我也。噫。彼二公欲閒之心。非后于我。而今日之閒。独不能无让于我。我之欲閒而未得者。亦有年。而幸今日之偶然得閒。而亦非所以计取力求也。其所谓自然而得閒。而欲閒者未必閒者。果不诬。呜呼。世之捐金钱营亭墅者。大是有力者事。而其所以营之者。亦有沈公之意。而凡诸宽閒之地。敞豁之搆。问其主之见在之否乎。则率无人焉。而其目谋心会之状。一任过客之临赏何者。显位重禄。有足蛊心。而江山风月。未暇取览。故富贵者。未尝不有欲閒之念。虽有欲閒之念。而无得閒之人。是亦有自然者存而然欤。抑富贵之有优于閒而然欤。然而历观古今。富贵者常多。閒者常小。则是知自然而得閒。抑有难于自然而得富贵欤。若我今日之閒。可谓其自然之会。而 二公无今日之閒。亦可谓不得其自然之会欤。白下集卷之十
跋
梧阴集跋
先祖文靖公。以德学功业。为 穆陵中兴元辅。其于不朽之事备矣。独其平日所著述。尽轶于壬辰兵燹。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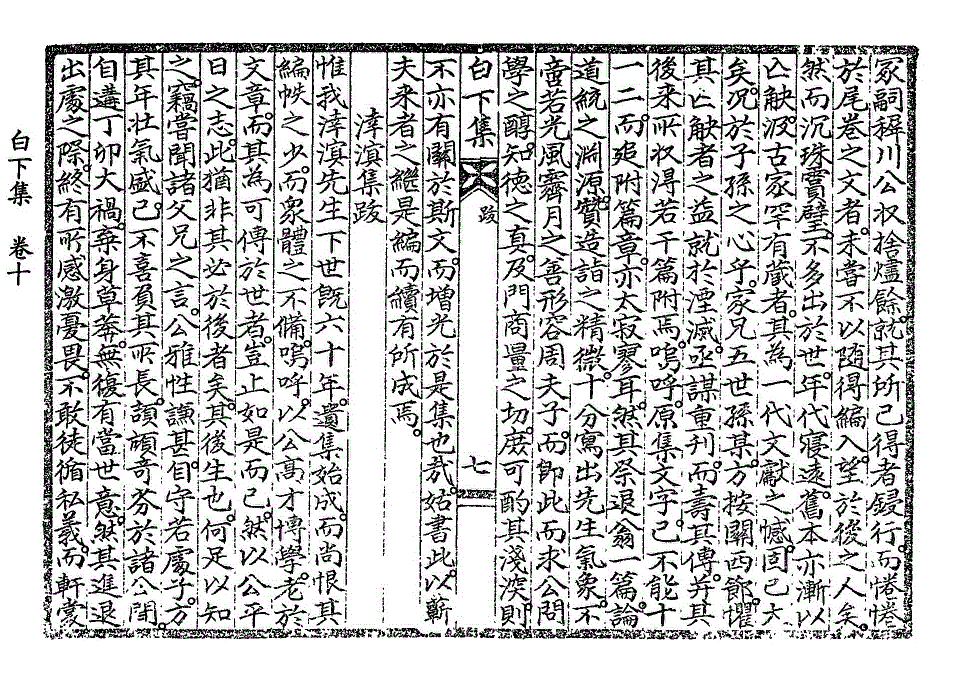 冢嗣稚川公收舍烬馀。就其所已得者锓行。而惓惓于尾卷之文者。未尝不以随得编入。望于后之人矣。然而沉珠霣璧。不多出于世。年代寝远。旧本亦渐以亡觖。汲古家罕有藏者。其为一代文献之憾。固已大矣。况于子孙之心乎。家兄五世孙某。方按关西节。惧其亡觖者之益就于湮灭。亟谋重刊。而寿其传。并其后来所收得若干篇附焉。呜呼。原集文字。已不能十一二。而追附篇章。亦太寂寥耳。然其祭退翁一篇。论道统之渊源。赞造诣之精微。十分写出先生气象。不啻若光风霁月之善形容周夫子。而即此而求公问学之醇。知德之真。及门商量之切。庶可酌其浅深。则不亦有关于斯文。而增光于是集也哉。姑书此。以蕲夫来者之继是编而续有所成焉。
冢嗣稚川公收舍烬馀。就其所已得者锓行。而惓惓于尾卷之文者。未尝不以随得编入。望于后之人矣。然而沉珠霣璧。不多出于世。年代寝远。旧本亦渐以亡觖。汲古家罕有藏者。其为一代文献之憾。固已大矣。况于子孙之心乎。家兄五世孙某。方按关西节。惧其亡觖者之益就于湮灭。亟谋重刊。而寿其传。并其后来所收得若干篇附焉。呜呼。原集文字。已不能十一二。而追附篇章。亦太寂寥耳。然其祭退翁一篇。论道统之渊源。赞造诣之精微。十分写出先生气象。不啻若光风霁月之善形容周夫子。而即此而求公问学之醇。知德之真。及门商量之切。庶可酌其浅深。则不亦有关于斯文。而增光于是集也哉。姑书此。以蕲夫来者之继是编而续有所成焉。涬溟集跋
惟我涬溟先生下世既六十年。遗集始成。而尚恨其编帙之少。而众体之不备。呜呼。以公高才博学。老于文章。而其为可传于世者。岂止如是而已。然以公平日之志。此犹非其必于后者矣。其后生也。何足以知之。窃尝闻诸父兄之言。公雅性谦甚。自守若处子。方其年壮气盛。已不喜负其所长。颉颃奇芬于诸公间。自遘丁卯大祸。弃身草莽。无复有当世意。然其进退出处之际。终有所感激忧畏。不敢徒循私义。而轩裳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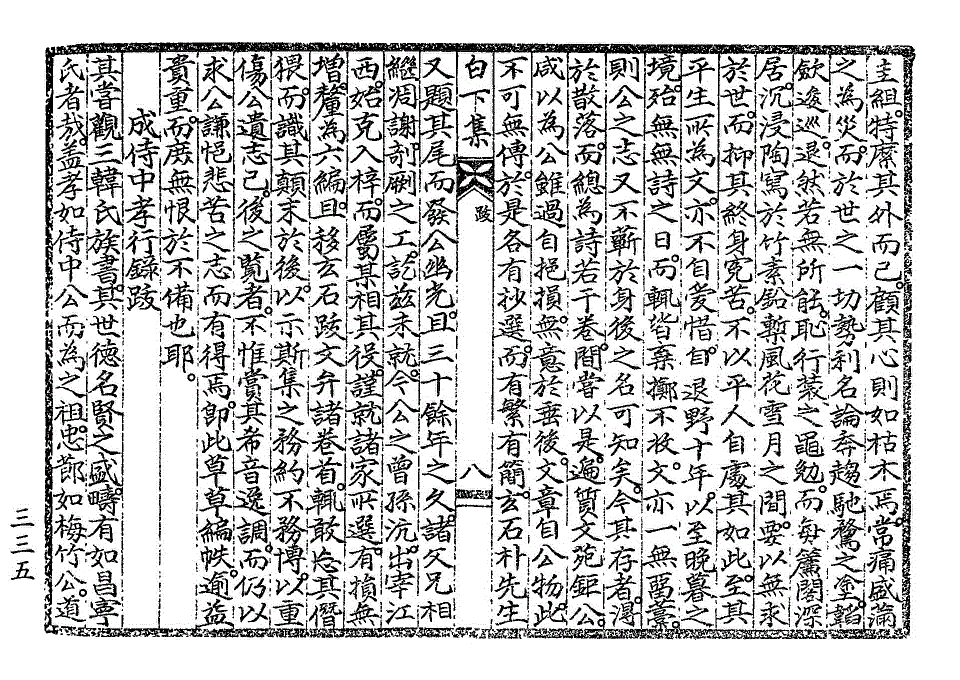 圭组。特縻其外而已。顾其心则如枯木焉。常痛盛满之为灾。而于世之一切势利名论奔趋驰骛之涂。韬敛逡巡。退然若无所能。耻行装之黾勉。而每帘阁深居。沉浸陶写于竹素铅椠风花雪月之间。要以无求于世。而抑其终身冤苦。不以平人自处其如此。至其平生所为文。亦不自爱惜。自退野十年。以至晚暮之境。殆无无诗之日。而辄皆弃掷不收。文亦一无留藁。则公之志又不蕲于身后之名可知矣。今其存者。得于散落。而总为诗若干卷。间尝以是。遍质文苑钜公。咸以为公虽过自挹损。无意于垂后。文章自公物。此不可无传。于是各有抄选。而有繁有简。玄石朴先生又题其尾而发公幽光。且三十馀年之久。诸父兄相继凋谢。剞劂之工。讫玆未就。今公之曾孙沆。出宰江西。始克入梓。而属某相其役。谨就诸家所选。有损无增。釐为六编。且移玄石跋文弁诸卷首。辄敢忘其僭猥。而识其颠末于后。以示斯集之务约不务博。以重伤公遗志已。后之览者。不惟赏其希音逸调。而仍以求公谦悒悲苦之志而有得焉。即此草草编帙。逾益贵重。而庶无恨于不备也耶。
圭组。特縻其外而已。顾其心则如枯木焉。常痛盛满之为灾。而于世之一切势利名论奔趋驰骛之涂。韬敛逡巡。退然若无所能。耻行装之黾勉。而每帘阁深居。沉浸陶写于竹素铅椠风花雪月之间。要以无求于世。而抑其终身冤苦。不以平人自处其如此。至其平生所为文。亦不自爱惜。自退野十年。以至晚暮之境。殆无无诗之日。而辄皆弃掷不收。文亦一无留藁。则公之志又不蕲于身后之名可知矣。今其存者。得于散落。而总为诗若干卷。间尝以是。遍质文苑钜公。咸以为公虽过自挹损。无意于垂后。文章自公物。此不可无传。于是各有抄选。而有繁有简。玄石朴先生又题其尾而发公幽光。且三十馀年之久。诸父兄相继凋谢。剞劂之工。讫玆未就。今公之曾孙沆。出宰江西。始克入梓。而属某相其役。谨就诸家所选。有损无增。釐为六编。且移玄石跋文弁诸卷首。辄敢忘其僭猥。而识其颠末于后。以示斯集之务约不务博。以重伤公遗志已。后之览者。不惟赏其希音逸调。而仍以求公谦悒悲苦之志而有得焉。即此草草编帙。逾益贵重。而庶无恨于不备也耶。成侍中孝行录跋
其尝观三韩氏族书。其世德名贤之盛。畴有如昌宁氏者哉。盖孝如侍中公而为之祖。忠节如梅竹公。道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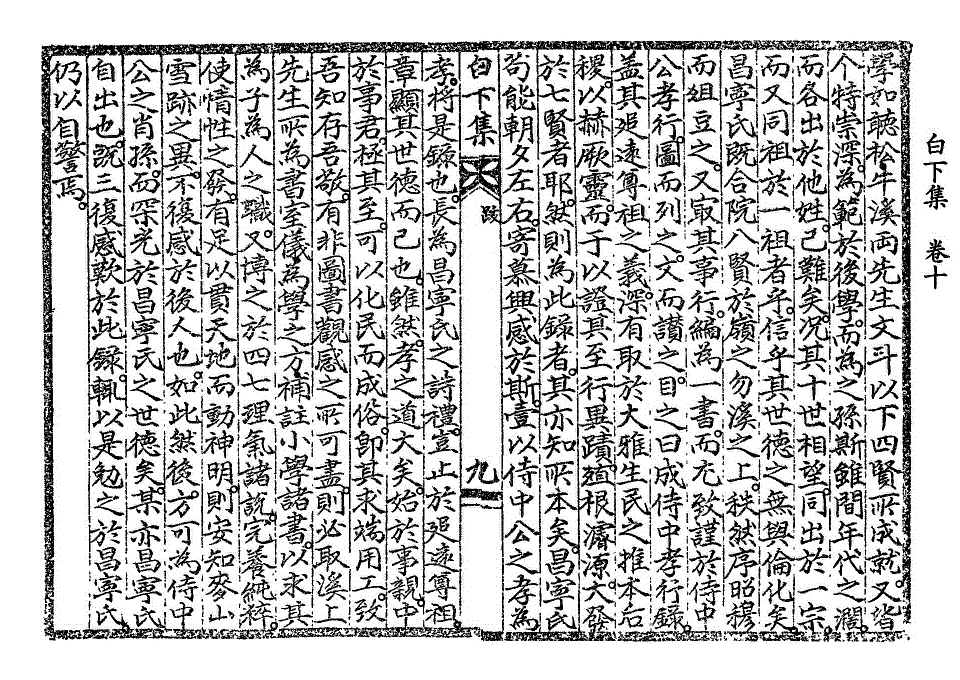 学如听松,牛溪两先生文斗以下四贤所成就。又皆个特崇深。为范于后学。而为之孙斯虽间年代之阔。而各出于他姓。已难矣。况其十世相望。同出于一宗。而又同祖于一祖者乎。信乎其世德之无与伦化矣。昌宁氏既合院八贤于岭之勿溪之上。秩然序昭穆而俎豆之。又最其事行。编为一书。而尤致谨于侍中公孝行。图而列之。文而赞之。目之曰成侍中孝行录。盖其追远尊祖之义。深有取于大雅生民之推本后稷。以赫厥灵。而于以證其至行异迹。殖根浚源。大发于七贤者耶。然则为此录者。其亦知所本矣。昌宁氏苟能朝夕左右。寄慕兴感于斯。壹以侍中公之孝为孝。将是录也。长为昌宁氏之诗礼。岂止于追远尊祖。章显其世德而已也。虽然。孝之道大矣。始于事亲。中于事君。极其至。可以化民而成俗。即其求端用工。致吾知存吾敬。有非图书观感之所可尽。则必取溪上先生所为书室仪,为学之方,补注小学诸书。以求其为子为人之职。又博之于四七理气诸说。完养纯粹。使情性之发。有足以贯天地而动神明。则安知麦山雪迹之异。不复感于后人也。如此然后。方可为侍中公之肖孙。而深光于昌宁氏之世德矣。某亦昌宁氏自出也。既三复感叹于此录。辄以是勉之于昌宁氏。仍以自警焉。
学如听松,牛溪两先生文斗以下四贤所成就。又皆个特崇深。为范于后学。而为之孙斯虽间年代之阔。而各出于他姓。已难矣。况其十世相望。同出于一宗。而又同祖于一祖者乎。信乎其世德之无与伦化矣。昌宁氏既合院八贤于岭之勿溪之上。秩然序昭穆而俎豆之。又最其事行。编为一书。而尤致谨于侍中公孝行。图而列之。文而赞之。目之曰成侍中孝行录。盖其追远尊祖之义。深有取于大雅生民之推本后稷。以赫厥灵。而于以證其至行异迹。殖根浚源。大发于七贤者耶。然则为此录者。其亦知所本矣。昌宁氏苟能朝夕左右。寄慕兴感于斯。壹以侍中公之孝为孝。将是录也。长为昌宁氏之诗礼。岂止于追远尊祖。章显其世德而已也。虽然。孝之道大矣。始于事亲。中于事君。极其至。可以化民而成俗。即其求端用工。致吾知存吾敬。有非图书观感之所可尽。则必取溪上先生所为书室仪,为学之方,补注小学诸书。以求其为子为人之职。又博之于四七理气诸说。完养纯粹。使情性之发。有足以贯天地而动神明。则安知麦山雪迹之异。不复感于后人也。如此然后。方可为侍中公之肖孙。而深光于昌宁氏之世德矣。某亦昌宁氏自出也。既三复感叹于此录。辄以是勉之于昌宁氏。仍以自警焉。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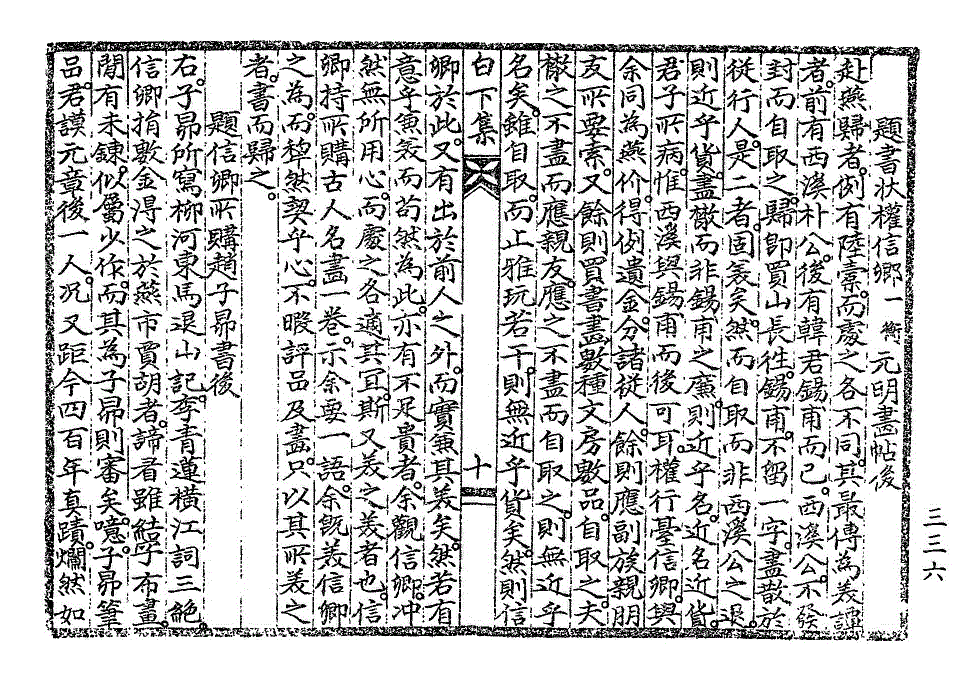 题书状权信卿(一衡)元明画帖后
题书状权信卿(一衡)元明画帖后赴燕归者。例有陆橐。而处之各不同。其最传为美谭者。前有西溪朴公。后有韩君锡甫而已。西溪公。不发封而自取之。归即买山长往。锡甫。不留一字。尽散于从行人。是二者。固美矣。然而自取而非西溪公之退。则近乎货。尽散而非锡甫之廉。则近乎名。近名近货。君子所病。惟西溪与锡甫而后可耳。权行台信卿。与余同为燕价。得例遗金。分诸从人。馀则应副族亲朋友所要索。又馀则买书画数种文房数品。自取之。夫散之不尽而应亲友。应之不尽而自取之。则无近乎名矣。虽自取。而止雅玩若干。则无近乎货矣。然则信卿于此。又有出于前人之外。而实兼其美矣。然若有意乎兼美而苟然为此。亦有不足贵者。余观信卿。冲然无所用心。而处之各适其宜。斯又美之美者也。信卿持所购古人名画一卷。示余要一语。余既美信卿之为。而犁然契乎心。不暇评品及画。只以其所美之者。书而归之。
题信卿所购赵子昂书后
右。子昂所写柳河东马退山记。李青莲横江词三绝。信卿捐数金得之于燕市贾胡者。谛看虽结字布画。閒有未鍊。似属少作。而其为子昂则审矣。噫。子昂笔品。君谟元章后一人。况又距今四百年真迹。烂然如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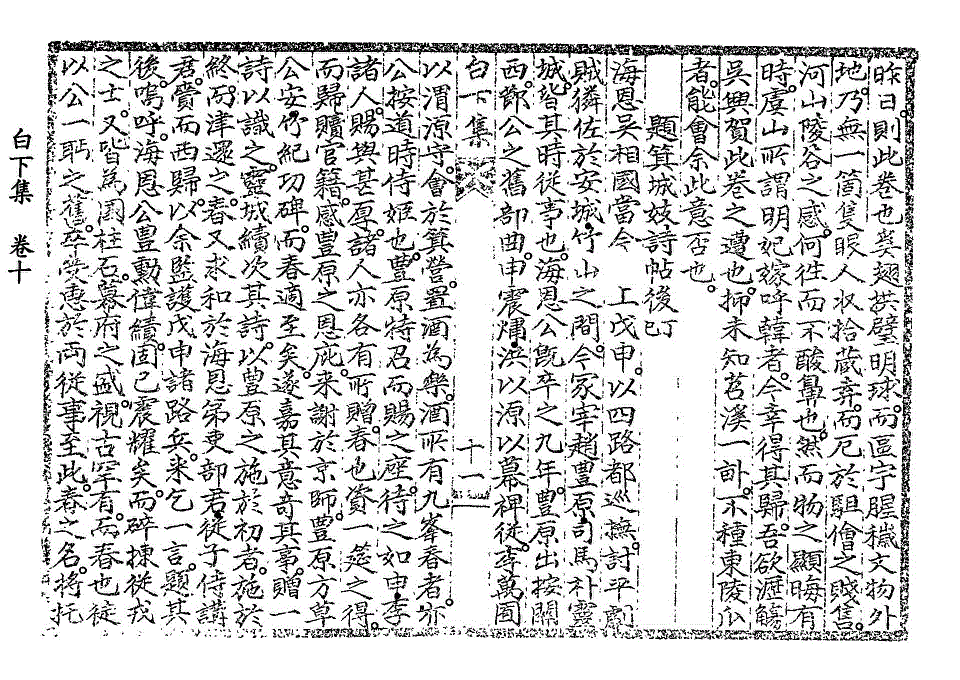 昨日。则此卷也奚翅拱璧明球。而区宇腥秽文物外地。乃无一个只眼人收拾藏弆。而厄于驵侩之贱售。河山陵谷之感。何往而不酸鼻也。然而物之显晦有时。虞山所谓明妃嫁呼韩者。今幸得其归。吾欲沥觞吴兴贺此卷之遭也。抑未知苕溪一𤱈。不种东陵瓜者。能会余此意否也。
昨日。则此卷也奚翅拱璧明球。而区宇腥秽文物外地。乃无一个只眼人收拾藏弆。而厄于驵侩之贱售。河山陵谷之感。何往而不酸鼻也。然而物之显晦有时。虞山所谓明妃嫁呼韩者。今幸得其归。吾欲沥觞吴兴贺此卷之遭也。抑未知苕溪一𤱈。不种东陵瓜者。能会余此意否也。题箕城妓诗帖后(丁巳)
海恩吴相国当今 上戊申。以四路都巡抚。讨平剧贼麟佐于安城,竹山之间。今冢宰赵礼原,司马朴灵城。皆其时从事也。海恩公既卒之九年。礼原出按关西。节公之旧部曲。申震熽,洪以源以幕裨从。李万囿以渭源守。会于箕营。置酒为乐。酒所有九峰春者。亦公按道时侍姬也。礼原特召而赐之座。待之如申,李诸人。赐与甚厚。诸人亦各有所赠。春也资一筵之得。而归赎官籍。感礼原之恩庇。来谢于京师。礼原方草公安,竹纪功碑。而春适至矣。遂嘉其意奇其事。赠一诗以识之。灵城续次其诗。以礼原之施于初者。施于终。而津还之。春又求和于海恩弟吏部君,从子侍讲君。赍而西归。以余监护戊申诸路兵。来乞一言。题其后。呜呼。海恩公礼勋伟绩。固已震耀矣。而碎拣从戎之士。又皆为国柱石。幕府之盛。视古罕有。而春也徒以公一眄之旧。卒受惠于两从事至此。春之名。将托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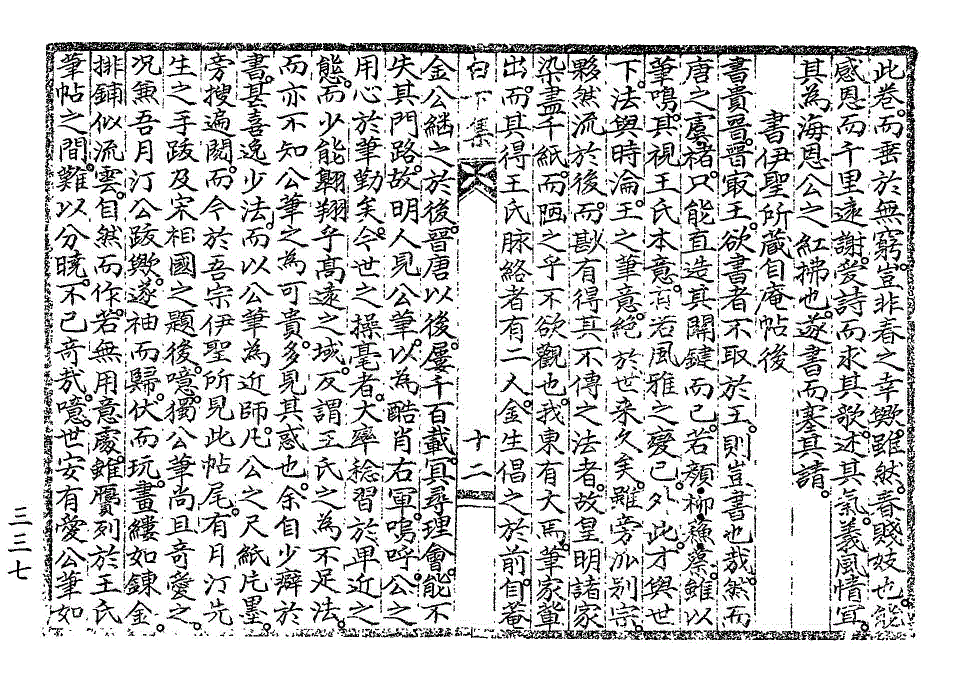 此卷。而垂于无穷。岂非春之幸欤。虽然。春贱妓也。能感恩而千里远谢。爱诗而求其歌。述其气。义风情宜。其为海恩公之红拂也。遂书而塞其请。
此卷。而垂于无穷。岂非春之幸欤。虽然。春贱妓也。能感恩而千里远谢。爱诗而求其歌。述其气。义风情宜。其为海恩公之红拂也。遂书而塞其请。书伊圣所藏自庵帖后
书贵晋。晋最王。欲书者不取于王。则岂书也哉。然而唐之虞,褚。只能直造其关键而已。若颜,柳,苏,蔡。虽以笔鸣。其视王氏本意。有若风雅之变已。外此。才与世下。法与时沦。王之笔意。绝于世来久矣。虽旁派别宗。夥然流于后。而鲜有得其不传之法者。故皇明诸家染尽千纸。而陋之乎不欲观也。我东有大焉。笔家辈出。而其得王氏脉络者有二人。金生倡之于前。自庵金公继之于后。晋唐以后。屡千百载。冥寻理会。能不失其门路。故明人见公笔。以为酷肖右军。呜呼。公之用心于笔勤矣。今世之操毫者。大率稔习于卑近之态。而少能翱翔乎高远之域。反谓王氏之为不足法。而亦不知公笔之为可贵。多见其惑也。余自少癖于书。甚喜逸少法。而以公笔为近师。凡公之尺纸片墨。旁搜遍阅。而今于吾宗伊圣所见此帖尾。有月汀先生之手跋及宋相国之题后。噫。独公笔尚且奇爱之。况兼吾月汀公跋欤。遂袖而归。伏而玩。画缕如鍊金。排铺似流云。自然而作。若无用意处。虽赝列于王氏笔帖之间。难以分晓。不已奇哉。噫。世安有爱公笔如
白下集卷之十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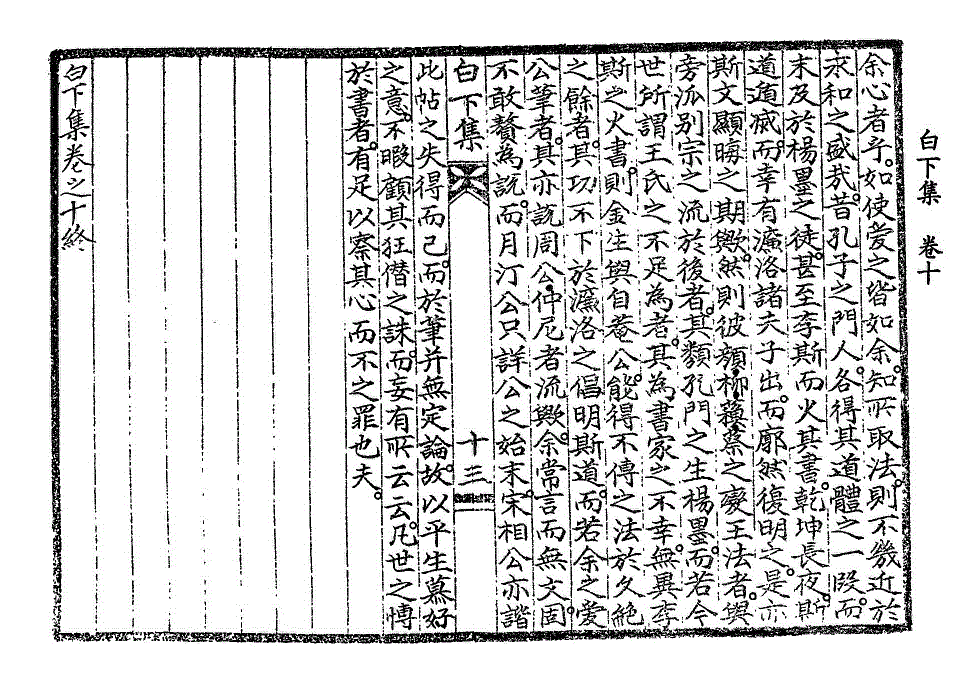 余心者乎。如使爱之皆如余。知所取法。则不几近于永和之盛哉。昔孔子之门人。各得其道体之一段。而末及于杨墨之徒。甚至李斯而火其书。乾坤长夜。斯道遁灭。而幸有濂洛诸夫子出。而廓然复明之。是亦斯文显晦之期欤。然则彼颜,柳,苏,蔡之变王法者。与旁派别宗之流于后者。其类孔门之生杨墨。而若今世所谓王氏之不足为者。其为书家之不幸。无异李斯之火书。则金生与自庵公。能得不传之法于久绝之馀者。其功不下于濂洛之倡明斯道。而若余之爱公笔者。其亦说周公,仲尼者流欤。余常言而无文。固不敢赘为说。而月汀公只详公之始末。宋相公亦谐此帖之失得而已。而于笔并无定论。故以平生慕好之意。不暇顾其狂僭之诛。而妄有所云云。凡世之博于书者。有足以察其心而不之罪也夫。
余心者乎。如使爱之皆如余。知所取法。则不几近于永和之盛哉。昔孔子之门人。各得其道体之一段。而末及于杨墨之徒。甚至李斯而火其书。乾坤长夜。斯道遁灭。而幸有濂洛诸夫子出。而廓然复明之。是亦斯文显晦之期欤。然则彼颜,柳,苏,蔡之变王法者。与旁派别宗之流于后者。其类孔门之生杨墨。而若今世所谓王氏之不足为者。其为书家之不幸。无异李斯之火书。则金生与自庵公。能得不传之法于久绝之馀者。其功不下于濂洛之倡明斯道。而若余之爱公笔者。其亦说周公,仲尼者流欤。余常言而无文。固不敢赘为说。而月汀公只详公之始末。宋相公亦谐此帖之失得而已。而于笔并无定论。故以平生慕好之意。不暇顾其狂僭之诛。而妄有所云云。凡世之博于书者。有足以察其心而不之罪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