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耐斋集卷之四 第 x 页
耐斋集卷之四(南阳洪泰猷伯亨甫 著)
记
记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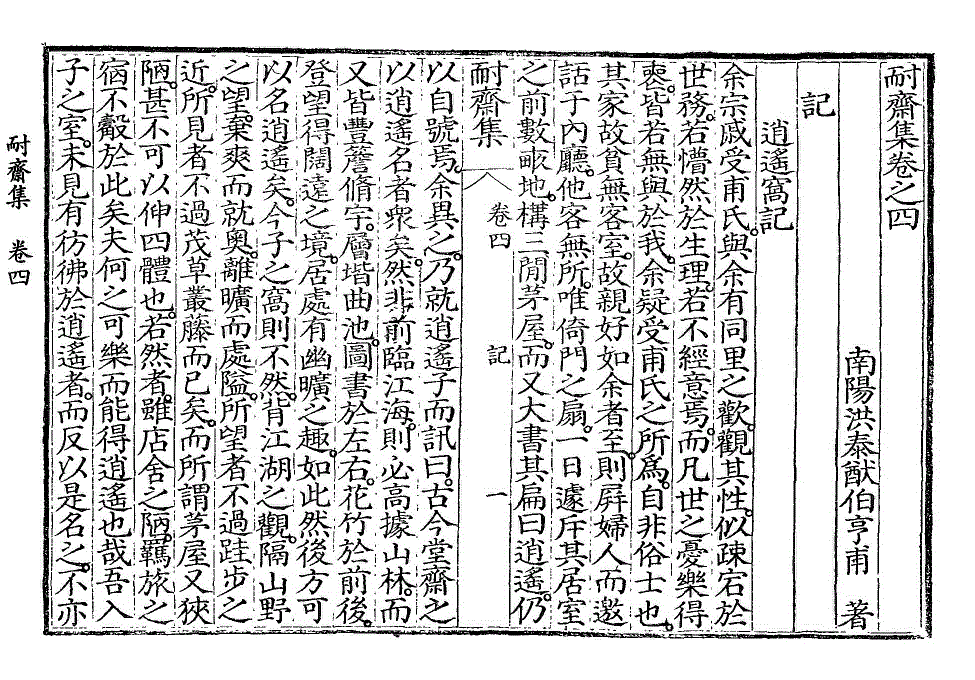 逍遥窝记
逍遥窝记余宗戚受甫氏。与余有同里之欢。观其性。似疏宕于世务。若懵然于生理。若不经意焉。而凡世之忧乐得丧。皆若无与于我。余疑受甫氏之所为。自非俗士也。其家故贫无客室。故亲好如余者至。则屏妇人而邀话于内厅。他客无所。唯倚门之扇。一日遽斥其居室之前数亩地。构三间茅屋。而又大书其扁曰逍遥。仍以自号焉。余异之。乃就逍遥子而讯曰。古今堂斋之以逍遥名者众矣。然非前临江海。则必高据山林。而又皆丰檐脩宇。层阶曲池。图书于左右。花竹于前后。登望得阔远之境。居处有幽旷之趣。如此然后方可以名逍遥矣。今子之窝则不然。背江湖之观。隔山野之望。弃爽而就奥。离旷而处隘。所望者不过跬步之近。所见者不过茂草丛藤而已矣。而所谓茅屋又狭陋。甚不可以伸四体也。若然者。虽店舍之陋。羁旅之宿不觳于此矣夫何之可乐而能得逍遥也哉吾入子之室。未见有彷佛于逍遥者。而反以是名之。不亦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3L 页
 怪矣乎。逍遥子犹然而笑曰。吾求逍遥于内子。求逍遥于外乎。彼爱江海山林者。以江海山林逍遥者也。彼有丰檐脩宇者。以丰檐脩宇逍遥者也。皆外也。非内也。若人也。方其自谓逍遥之时。啸咏徘徊。极意为娱。若无以易此者。一有得丧欣戚挂于其心。则汩汩然其中已胶扰矣。顾何有于閒适之境哉。今余所以逍遥者则异于是。与心谋不求于身。与神游不谋于心。放则如云如风。无碍无滞。止则如枯株如死灰。无言无动。当此之时。不知形骸之为吾形骸也。何暇知有得丧欣戚也哉。且吾居虽陋。犹可以伸吾膝矣。独不得梦乎。梦不得为蝴蝶乎。蝴蝶不得为我乎。我不得为蝴蝶乎。然则蝴蝶与我。犹不可知。又何暇知江海山林丰檐脩宇与夫余之茅屋也哉。吾闻其言。类有道者。逍遥子。其学庄老者欤。余亦从逍遥子游。自谓有江湖优游之乐。而犹不能忘情于忧乐得丧之间。则今逍遥子之论警余者。多记其语而书诸座右。盖将以自省也。逍遥子见而请题其壁。仍写以与之。
怪矣乎。逍遥子犹然而笑曰。吾求逍遥于内子。求逍遥于外乎。彼爱江海山林者。以江海山林逍遥者也。彼有丰檐脩宇者。以丰檐脩宇逍遥者也。皆外也。非内也。若人也。方其自谓逍遥之时。啸咏徘徊。极意为娱。若无以易此者。一有得丧欣戚挂于其心。则汩汩然其中已胶扰矣。顾何有于閒适之境哉。今余所以逍遥者则异于是。与心谋不求于身。与神游不谋于心。放则如云如风。无碍无滞。止则如枯株如死灰。无言无动。当此之时。不知形骸之为吾形骸也。何暇知有得丧欣戚也哉。且吾居虽陋。犹可以伸吾膝矣。独不得梦乎。梦不得为蝴蝶乎。蝴蝶不得为我乎。我不得为蝴蝶乎。然则蝴蝶与我。犹不可知。又何暇知江海山林丰檐脩宇与夫余之茅屋也哉。吾闻其言。类有道者。逍遥子。其学庄老者欤。余亦从逍遥子游。自谓有江湖优游之乐。而犹不能忘情于忧乐得丧之间。则今逍遥子之论警余者。多记其语而书诸座右。盖将以自省也。逍遥子见而请题其壁。仍写以与之。二橡亭记
循汉而上求湖山清远之区。唯黄骊之梨浦为最而余居之。然是胜也。梨浦之村皆有焉。不足异矣。村之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4H 页
 南百馀步。得所谓近汀者。既同有梨浦村之有矣。而又得清溪锦石。以专一丘潇洒之趣。则近汀之胜。又梨浦之最也。是则吾友申明瑞居之。余诚爱而乐焉。每春夏之夕。挐小舟。由江入溪。则澄流铺沙。奇岩峙岛。林木翳然而幽。禽鸟嘤然而和。沿洄上下。心旷神清。殊不知由咫尺得里闬而以为异区别界也。明瑞亦韵士。啸咏以自乐。而日不离乎玆溪之上。故余往焉。不待有招呼。而已在洲边岩上矣。相与命酒吟诗。尽兴而返。余与明瑞之游是溪。甚适而欢也。岸上有二橡树。苍老可爱。方夏盛炎。常就是而荫焉。然有时风雨骤至。索然败兴而归者数矣。明瑞思欲朝夕于此。而惜无以庇也。谋数椽之亭者久。曩岁余有事于京。经时而返。则溪头茅栋。果突然而起矣。余急就明瑞而贺问所以扁者。则曰二橡。余曰。善哉扁也。当无亭时。明瑞之徘徊啸咏。以为宴息之所者。固唯二橡是赖。今茅亭成矣。而乃能不别求美名。又扁以二橡。则明瑞之不忘其素。可谓贤矣。观世之士。一有得志。骄傲自恣。尽忘其贫贱之时者多矣。闻明瑞之风。岂不少愧也耶。地诚胜矣。亦因人而名。则沂溪虽佳。将必得明瑞之贤而愈名于乡矣。然则至今百有馀年。
南百馀步。得所谓近汀者。既同有梨浦村之有矣。而又得清溪锦石。以专一丘潇洒之趣。则近汀之胜。又梨浦之最也。是则吾友申明瑞居之。余诚爱而乐焉。每春夏之夕。挐小舟。由江入溪。则澄流铺沙。奇岩峙岛。林木翳然而幽。禽鸟嘤然而和。沿洄上下。心旷神清。殊不知由咫尺得里闬而以为异区别界也。明瑞亦韵士。啸咏以自乐。而日不离乎玆溪之上。故余往焉。不待有招呼。而已在洲边岩上矣。相与命酒吟诗。尽兴而返。余与明瑞之游是溪。甚适而欢也。岸上有二橡树。苍老可爱。方夏盛炎。常就是而荫焉。然有时风雨骤至。索然败兴而归者数矣。明瑞思欲朝夕于此。而惜无以庇也。谋数椽之亭者久。曩岁余有事于京。经时而返。则溪头茅栋。果突然而起矣。余急就明瑞而贺问所以扁者。则曰二橡。余曰。善哉扁也。当无亭时。明瑞之徘徊啸咏。以为宴息之所者。固唯二橡是赖。今茅亭成矣。而乃能不别求美名。又扁以二橡。则明瑞之不忘其素。可谓贤矣。观世之士。一有得志。骄傲自恣。尽忘其贫贱之时者多矣。闻明瑞之风。岂不少愧也耶。地诚胜矣。亦因人而名。则沂溪虽佳。将必得明瑞之贤而愈名于乡矣。然则至今百有馀年。耐斋集卷之四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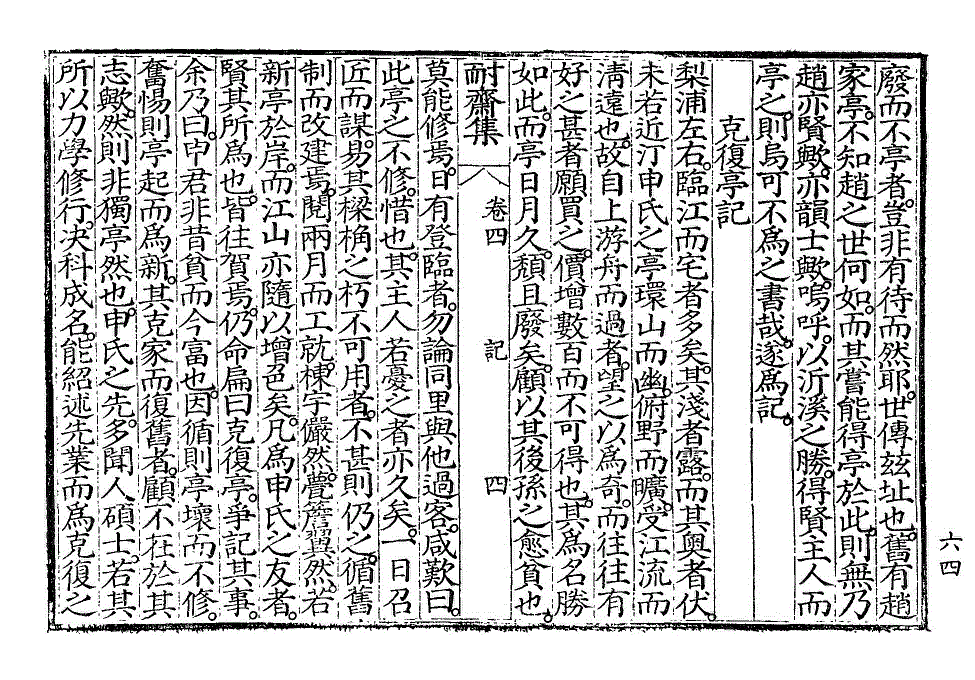 废而不亭者。岂非有待而然耶。世传玆址也。旧有赵家亭。不知赵之世何如。而其尝能得亭于此。则无乃赵亦贤欤。亦韵士欤。呜呼。以沂溪之胜。得贤主人而亭之。则乌可不为之书哉。遂为记。
废而不亭者。岂非有待而然耶。世传玆址也。旧有赵家亭。不知赵之世何如。而其尝能得亭于此。则无乃赵亦贤欤。亦韵士欤。呜呼。以沂溪之胜。得贤主人而亭之。则乌可不为之书哉。遂为记。克复亭记
梨浦左右。临江而宅者多矣。其浅者露。而其奥者伏。未若近汀申氏之亭环山而幽。俯野而旷。受江流而清远也。故自上游舟而过者。望之以为奇。而往往有好之甚者愿买之。价增数百而不可得也。其为名胜如此。而亭日月久。颓且废矣。顾以其后孙之愈贫也。莫能修焉。日有登临者。勿论同里与他过客。咸叹曰。此亭之不修。惜也。其主人若忧之者亦久矣。一日召匠而谋。易其梁桷之朽不可用者。不甚则仍之。循旧制而改建焉。阅两月而工就。栋宇俨然。甍檐翼然。若新亭于岸。而江山亦随以增色矣。凡为申氏之友者。贤其所为也。皆往贺焉。仍命扁曰克复亭。争记其事。余乃曰。申君非昔贫而今富也。因循则亭坏而不修。奋惕则亭起而为新。其克家而复旧者。顾不在于其志欤。然则非独亭然也。申氏之先。多闻人硕士。若其所以力学修行。决科成名。能绍述先业而为克复之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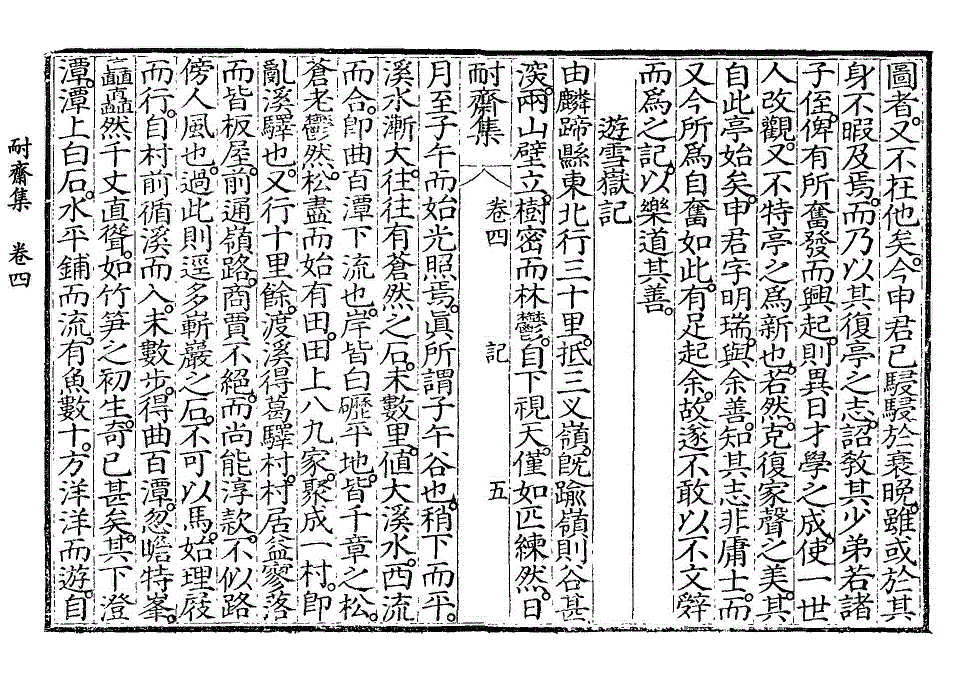 图者。又不在他矣。今申君已骎骎于衰晚。虽或于其身不暇及焉。而乃以其复亭之志。诏教其少弟若诸子侄。俾有所奋发而兴起。则异日才学之成。使一世人改观。又不特亭之为新也。若然。克复家声之美。其自此亭始矣。申君字明瑞。与余善。知其志非庸士。而又今所为自奋如此。有足起余。故遂不敢以不文辞而为之记。以乐道其善。
图者。又不在他矣。今申君已骎骎于衰晚。虽或于其身不暇及焉。而乃以其复亭之志。诏教其少弟若诸子侄。俾有所奋发而兴起。则异日才学之成。使一世人改观。又不特亭之为新也。若然。克复家声之美。其自此亭始矣。申君字明瑞。与余善。知其志非庸士。而又今所为自奋如此。有足起余。故遂不敢以不文辞而为之记。以乐道其善。游雪岳记
由麟蹄县东北行三十里。抵三叉岭。既踰岭则谷甚深。两山壁立。树密而林郁。自下视天。仅如匹练然。日月至子午而始光照焉。真所谓子午谷也。稍下而平。溪水渐大。往往有苍然之石。未数里。值大溪水。西流而合。即曲百潭下流也。岸皆白礰平地。皆千章之松。苍老郁然。松尽而始有田。田上八九家。聚成一村。即乱溪驿也。又行十里馀。渡溪得葛驿村。村居益寥落而皆板屋。前通岭路。商贾不绝。而尚能淳款。不似路傍人风也。过此则径多崭岩之石。不可以马。始理屐而行。自村前循溪而入。未数步。得曲百潭。忽瞻特峰。矗矗然千丈直耸。如竹笋之初生。奇已甚矣。其下澄潭。潭上白石。水平铺而流。有鱼数十。方洋洋而游。自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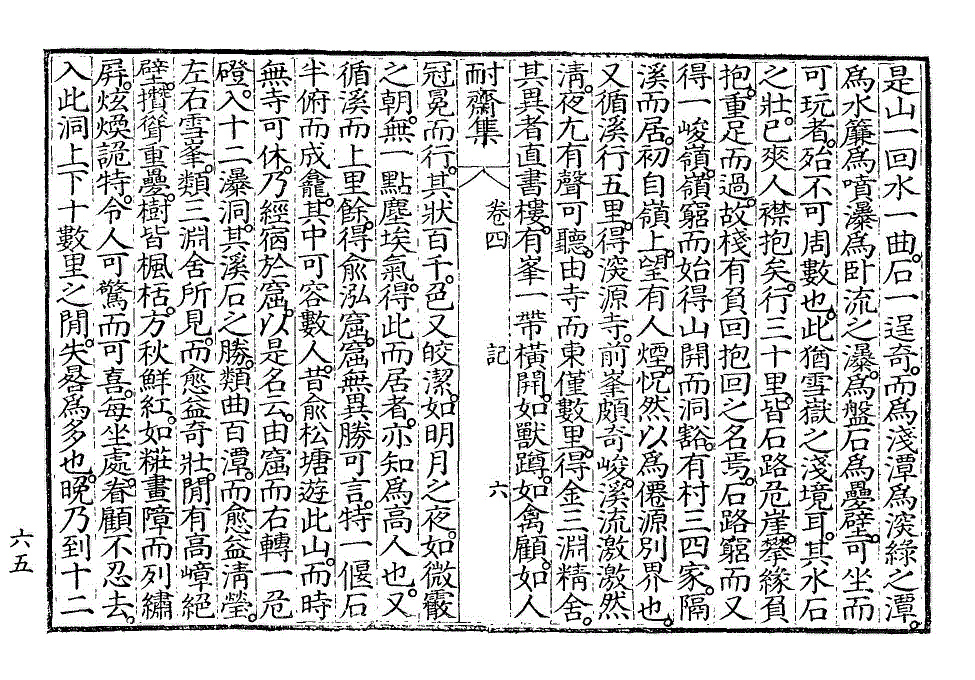 是山一回水一曲。石一逞奇。而为浅潭为深绿之潭。为水帘为喷瀑为卧流之瀑。为盘石为叠壁。可坐而可玩者。殆不可周数也。此犹雪岳之浅境耳。其水石之壮。已爽人襟抱矣。行三十里。皆石路危崖。攀缘负抱。重足而过。故栈有负回抱回之名焉。石路穷而又得一峻岭。岭穷而始得山开而洞豁。有村三四家。隔溪而居。初自岭上。望有人烟。恍然以为仙源别界也。又循溪行五里。得深源寺。前峰颇奇峻。溪流激激然清。夜尤有声可听。由寺而东仅数里。得金三渊精舍。其异者直书楼。有峰一带横开。如兽蹲。如禽顾。如人冠冕而行。其状百千。色又皎洁。如明月之夜。如微霰之朝。无一点尘埃气。得此而居者。亦知为高人也。又循溪而上里馀。得俞泓窟。窟无异胜可言。特一偃石半俯而成龛。其中可容数人。昔俞松塘游此山。而时无寺可休。乃经宿于窟。以是名云。由窟而右转一危磴。入十二瀑洞。其溪石之胜。类曲百潭。而愈益清莹。左右雪峰。类三渊舍所见。而愈益奇壮。间有高嶂绝壁。攒耸重叠。树皆枫栝。方秋鲜红。如妆画障而列绣屏。炫焕诡特。令人可惊而可喜。每坐处。眷顾不忍去。入此洞上下十数里之间。失晷为多也。晚乃到十二
是山一回水一曲。石一逞奇。而为浅潭为深绿之潭。为水帘为喷瀑为卧流之瀑。为盘石为叠壁。可坐而可玩者。殆不可周数也。此犹雪岳之浅境耳。其水石之壮。已爽人襟抱矣。行三十里。皆石路危崖。攀缘负抱。重足而过。故栈有负回抱回之名焉。石路穷而又得一峻岭。岭穷而始得山开而洞豁。有村三四家。隔溪而居。初自岭上。望有人烟。恍然以为仙源别界也。又循溪行五里。得深源寺。前峰颇奇峻。溪流激激然清。夜尤有声可听。由寺而东仅数里。得金三渊精舍。其异者直书楼。有峰一带横开。如兽蹲。如禽顾。如人冠冕而行。其状百千。色又皎洁。如明月之夜。如微霰之朝。无一点尘埃气。得此而居者。亦知为高人也。又循溪而上里馀。得俞泓窟。窟无异胜可言。特一偃石半俯而成龛。其中可容数人。昔俞松塘游此山。而时无寺可休。乃经宿于窟。以是名云。由窟而右转一危磴。入十二瀑洞。其溪石之胜。类曲百潭。而愈益清莹。左右雪峰。类三渊舍所见。而愈益奇壮。间有高嶂绝壁。攒耸重叠。树皆枫栝。方秋鲜红。如妆画障而列绣屏。炫焕诡特。令人可惊而可喜。每坐处。眷顾不忍去。入此洞上下十数里之间。失晷为多也。晚乃到十二耐斋集卷之四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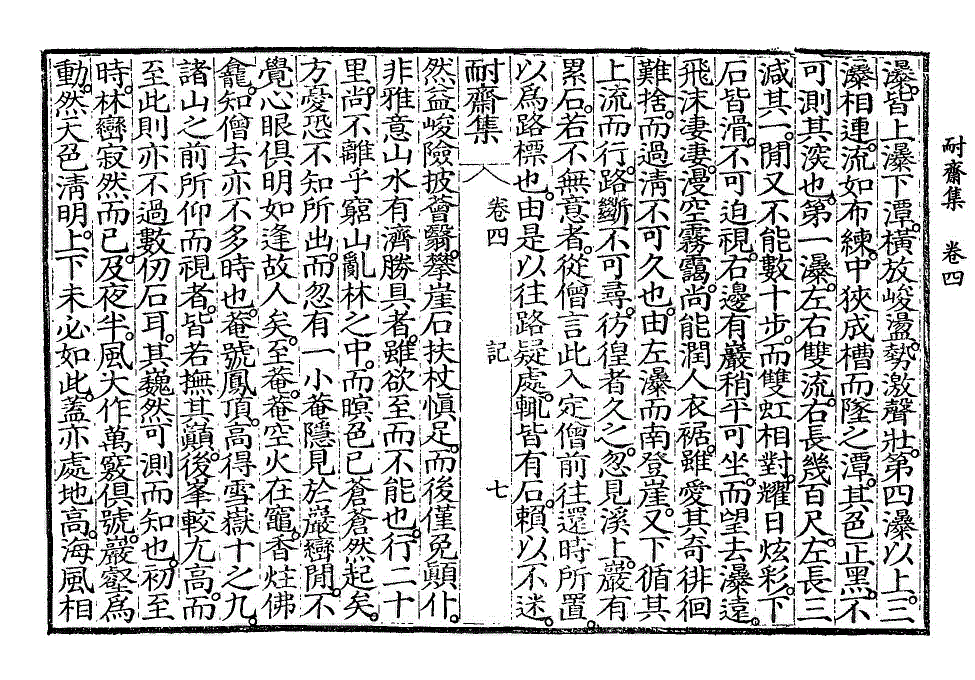 瀑。皆上瀑下潭。横放峻荡。势激声壮。第四瀑以上。三瀑相连。流如布练。中狭成槽而坠之潭。其色正黑。不可测其深也。第一瀑。左右双流。右长几百尺。左长三减其一。间又不能数十步。而双虹相对。耀日炫彩。下石皆滑。不可迫视。右边有岩稍平可坐。而望去瀑远。飞沫凄凄。漫空雾霭。尚能润人衣裾。虽爱其奇徘徊难舍。而过清不可久也。由左瀑而南登崖。又下循其上流而行。路断不可寻。彷徨者久之。忽见溪上。岩有累石。若不无意者。从僧言此入定僧前往还时所置。以为路标也。由是以往路疑处。辄皆有石。赖以不迷。然益峻险披荟翳。攀崖石扶杖慎足。而后仅免颠仆。非雅意山水有济胜具者。虽欲至而不能也。行二十里。尚不离乎穷山乱林之中。而暝色已苍苍然起矣。方忧恐不知所出。而忽有一小庵隐见于岩峦间。不觉心眼俱明如逢故人矣。至庵。庵空火在灶。香炷佛龛。知僧去亦不多时也。庵号凤顶。高得雪岳十之九。诸山之前所仰而视者。皆若抚其巅。后峰较尤高。而至此则亦不过数仞石耳。其巍然可测而知也。初至时。林峦寂然而已。及夜半。风大作万窍俱号。岩壑为动。然天色清明。上下未必如此。盖亦处地高。海风相
瀑。皆上瀑下潭。横放峻荡。势激声壮。第四瀑以上。三瀑相连。流如布练。中狭成槽而坠之潭。其色正黑。不可测其深也。第一瀑。左右双流。右长几百尺。左长三减其一。间又不能数十步。而双虹相对。耀日炫彩。下石皆滑。不可迫视。右边有岩稍平可坐。而望去瀑远。飞沫凄凄。漫空雾霭。尚能润人衣裾。虽爱其奇徘徊难舍。而过清不可久也。由左瀑而南登崖。又下循其上流而行。路断不可寻。彷徨者久之。忽见溪上。岩有累石。若不无意者。从僧言此入定僧前往还时所置。以为路标也。由是以往路疑处。辄皆有石。赖以不迷。然益峻险披荟翳。攀崖石扶杖慎足。而后仅免颠仆。非雅意山水有济胜具者。虽欲至而不能也。行二十里。尚不离乎穷山乱林之中。而暝色已苍苍然起矣。方忧恐不知所出。而忽有一小庵隐见于岩峦间。不觉心眼俱明如逢故人矣。至庵。庵空火在灶。香炷佛龛。知僧去亦不多时也。庵号凤顶。高得雪岳十之九。诸山之前所仰而视者。皆若抚其巅。后峰较尤高。而至此则亦不过数仞石耳。其巍然可测而知也。初至时。林峦寂然而已。及夜半。风大作万窍俱号。岩壑为动。然天色清明。上下未必如此。盖亦处地高。海风相耐斋集卷之四 第 66L 页
 激而然也。朝自庵左登塔台有大石。其上累塔如浮屠。僧云释迦佛舍利藏于是。转而向右。益高而豁前。望沧海迷茫无际。亦一壮观也。自此攀壁而下五六里。至稍平处。岩壁泉石之胜。亦不下于十二瀑之下流。又二十里馀。得闭门岩。最为此洞佳处。两壁削立。耸峙如门关然。若与尘世限矣。自岩而右。踰一峻巘。为五岁庵。峰峦之奇秀。尽三渊舍所见而较优云。逢雨狼狈。不可历寻为可恨也。循溪而下。复与俞泓窟会。游事亦至此而穷矣。凡游凤顶者。由窟而左。则先闭门而后十二瀑。由窟而右。则先十二瀑而后闭门。言游览次第。大抵如此。雪岳之为山。雄跨关东西。其阴则襄阳。其阳则麟蹄。襄之胜。称食堂瀑戒祖窟。而余未见者。麟之胜称曲百潭,深源寺,三渊精舍,十二瀑,凤顶庵,闭门庵。而皆余之所已详者。若论其峰峦泉石之奇。十二瀑为最也。余见名山多矣。惟金刚可与此山相伯仲。其他无有能与抗者。然金刚名播中华。而此山之胜。虽东人。知者盖寡。则此山实亦山之隐者也。故余详叙其胜如此。将以誇视乡里之朋游。而又开夫世之求名山水而未尽知者。同游者。宗人受甫其字。姨弟任君道彦其字。从侄李君振伯其字。
激而然也。朝自庵左登塔台有大石。其上累塔如浮屠。僧云释迦佛舍利藏于是。转而向右。益高而豁前。望沧海迷茫无际。亦一壮观也。自此攀壁而下五六里。至稍平处。岩壁泉石之胜。亦不下于十二瀑之下流。又二十里馀。得闭门岩。最为此洞佳处。两壁削立。耸峙如门关然。若与尘世限矣。自岩而右。踰一峻巘。为五岁庵。峰峦之奇秀。尽三渊舍所见而较优云。逢雨狼狈。不可历寻为可恨也。循溪而下。复与俞泓窟会。游事亦至此而穷矣。凡游凤顶者。由窟而左。则先闭门而后十二瀑。由窟而右。则先十二瀑而后闭门。言游览次第。大抵如此。雪岳之为山。雄跨关东西。其阴则襄阳。其阳则麟蹄。襄之胜。称食堂瀑戒祖窟。而余未见者。麟之胜称曲百潭,深源寺,三渊精舍,十二瀑,凤顶庵,闭门庵。而皆余之所已详者。若论其峰峦泉石之奇。十二瀑为最也。余见名山多矣。惟金刚可与此山相伯仲。其他无有能与抗者。然金刚名播中华。而此山之胜。虽东人。知者盖寡。则此山实亦山之隐者也。故余详叙其胜如此。将以誇视乡里之朋游。而又开夫世之求名山水而未尽知者。同游者。宗人受甫其字。姨弟任君道彦其字。从侄李君振伯其字。耐斋集卷之四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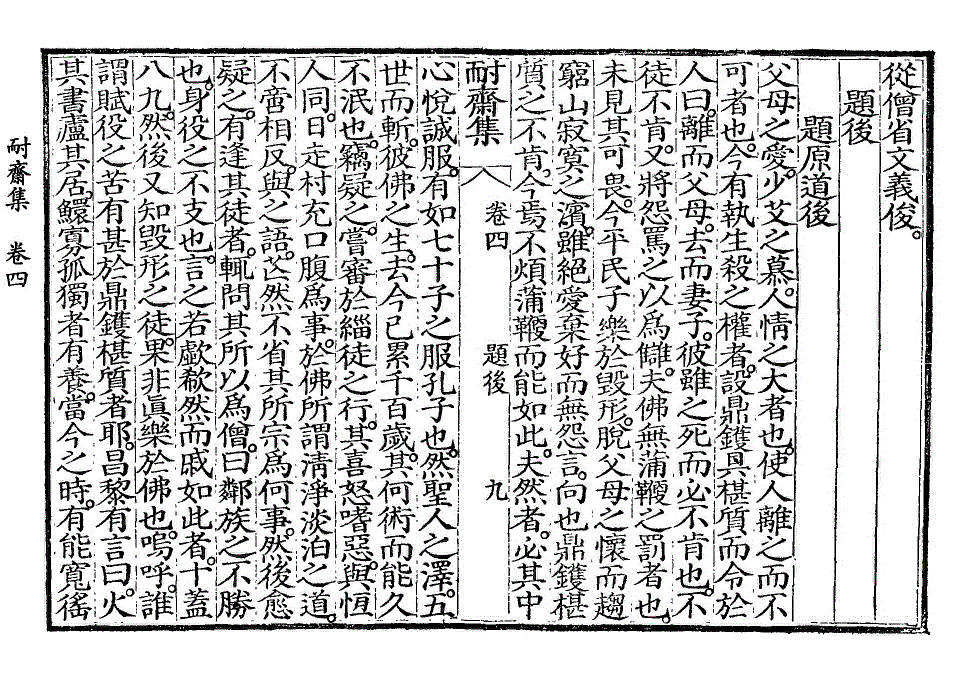 从僧省文义俊。
从僧省文义俊。耐斋集卷之四(南阳洪泰猷伯亨甫 著)
题后
题原道后
父母之爱。少艾之慕。人情之大者也。使人离之而不可者也。今有执生杀之权者。设鼎镬具椹质而令于人曰。离而父母。去而妻子。彼虽之死而必不肯也。不徒不肯。又将怨骂之以为雠。夫佛无蒲鞭之罚者也。未见其可畏。今平民子乐于毁形。脱父母之怀而趋穷山寂寞之滨。虽绝爱弃好而无怨言。向也鼎镬椹质之不肯。今焉不烦蒲鞭而能如此。夫然者。必其中心悦诚服。有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然圣人之泽。五世而斩。彼佛之生。去今已累千百岁。其何术而能久不泯也。窃疑之。尝审于缁徒之行。其喜怒嗜恶。与恒人同。日走村充口腹为事。于佛所谓清净淡泊之道。不啻相反。与之语。芒然不省其所宗为何事。然后愈疑之。有逢其徒者。辄问其所以为僧。曰邻族之不胜也。身役之不支也。言之若歔欷然而戚如此者。十盖八九。然后又知毁形之徒。果非真乐于佛也。呜呼。谁谓赋役之苦有甚于鼎镬椹质者耶。昌黎有言曰。火其书庐其居。鳏寡孤独者有养。当今之时。有能宽徭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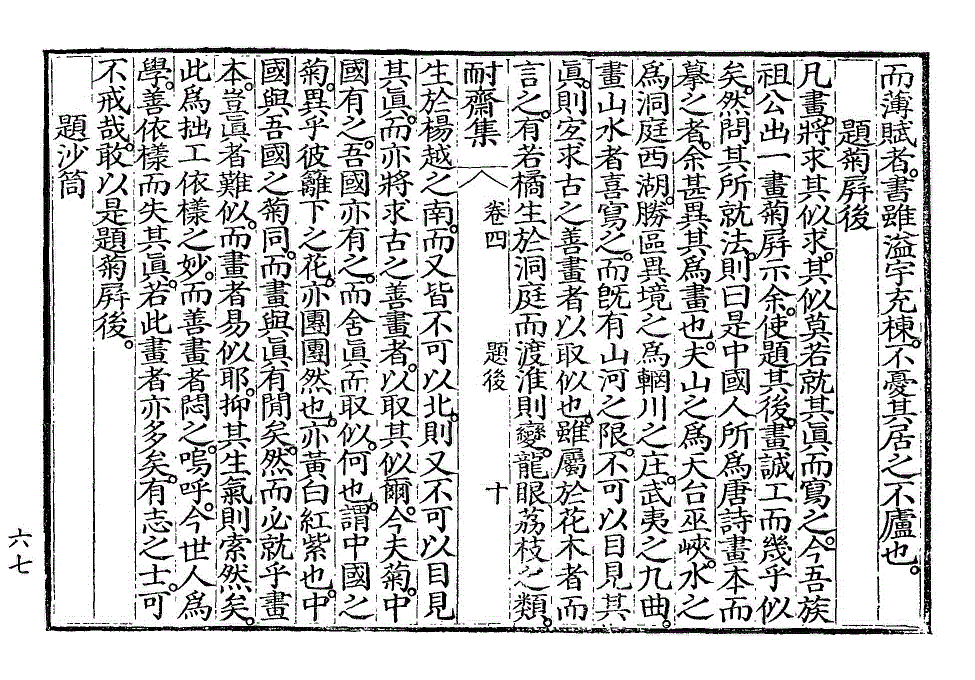 而薄赋者。书虽溢宇充栋。不忧其居之不庐也。
而薄赋者。书虽溢宇充栋。不忧其居之不庐也。题菊屏后
凡画。将求其似求。其似莫若就其真而写之。今吾族祖公出一画菊屏示余。使题其后。画诚工而几乎似矣。然问其所就法。则曰是中国人所为唐诗画本而摹之者。余甚异其为画也。夫山之为天台巫峡。水之为洞庭西湖。胜区异境之为辋川之庄。武夷之九曲。画山水者喜写之。而既有山河之限。不可以目见其真。则宜求古之善画者以取似也。虽属于花木者而言之。有若橘生于洞庭而渡淮则变。龙眼荔枝之类。生于杨越之南。而又皆不可以北。则又不可以目见其真。而亦将求古之善画者。以取其似尔。今夫菊。中国有之。吾国亦有之。而舍真而取似。何也。谓中国之菊。异乎彼篱下之花。亦团团然也。亦黄白红紫也。中国与吾国之菊同。而画与真有间矣。然而必就乎画本。岂真者难似。而画者易似耶。抑其生气则索然矣。此为拙工依样之妙。而善画者闷之。呜呼。今世人为学。善依样而失其真。若此画者亦多矣。有志之士。可不戒哉。敢以是题菊屏后。
题沙筒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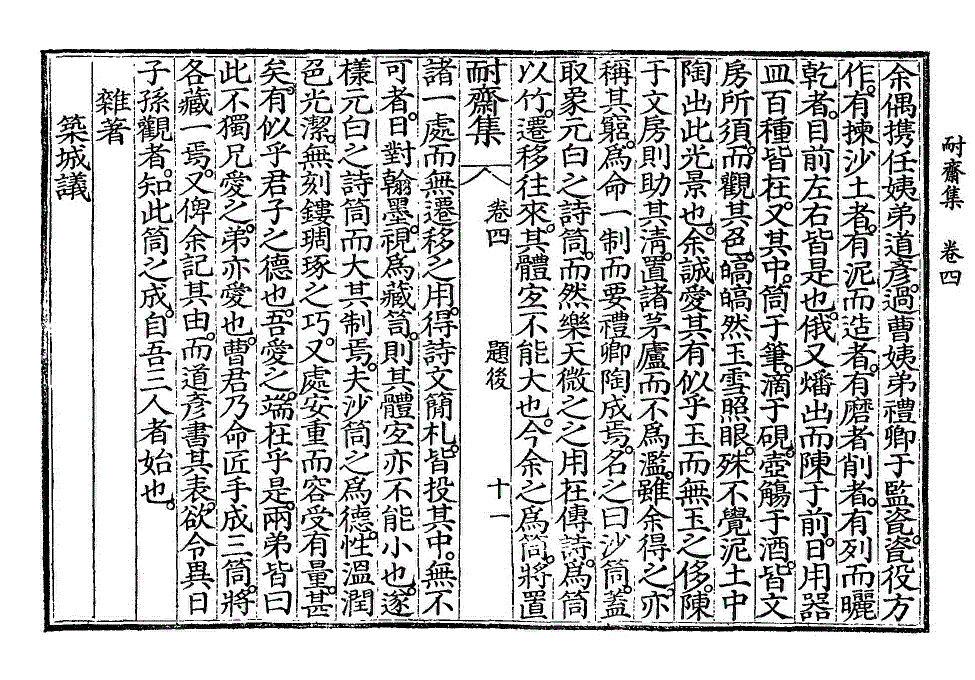 余偶携任姨弟道彦。过曹姨弟礼卿于监瓷。瓷役方作。有拣沙土者。有泥而造者。有磨者削者。有列而晒乾者。目前左右皆是也。俄又燔出而陈于前。日用器皿百种皆在。又其中。筒于笔。滴于砚。壶觞于酒。皆文房所须。而观其色。皓皓然玉雪照眼。殊不觉泥土中陶出此光景也。余诚爱其有似乎玉而无玉之侈。陈于文房则助其清。置诸茅庐而不为滥。虽余得之。亦称其穷。为命一制而要礼卿陶成焉。名之曰沙筒。盖取象元白之诗筒。而然乐天微之之用在传诗。为筒以竹。迁移往来。其体宜不能大也。今余之为筒。将置诸一处而无迁移之用。得诗文简札。皆投其中。无不可者。日对翰墨。视为藏笥。则其体宜亦不能小也。遂样元白之诗筒而大其制焉。夫沙筒之为德。性温润色光洁。无刻镂雕琢之巧。又处安重而容受有量。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吾爱之。端在乎是。两弟皆曰此不独兄爱之。弟亦爱也。曹君乃命匠手成三筒。将各藏一焉。又俾余记其由。而道彦书其表。欲令异日子孙观者。知此筒之成。自吾三人者始也。
余偶携任姨弟道彦。过曹姨弟礼卿于监瓷。瓷役方作。有拣沙土者。有泥而造者。有磨者削者。有列而晒乾者。目前左右皆是也。俄又燔出而陈于前。日用器皿百种皆在。又其中。筒于笔。滴于砚。壶觞于酒。皆文房所须。而观其色。皓皓然玉雪照眼。殊不觉泥土中陶出此光景也。余诚爱其有似乎玉而无玉之侈。陈于文房则助其清。置诸茅庐而不为滥。虽余得之。亦称其穷。为命一制而要礼卿陶成焉。名之曰沙筒。盖取象元白之诗筒。而然乐天微之之用在传诗。为筒以竹。迁移往来。其体宜不能大也。今余之为筒。将置诸一处而无迁移之用。得诗文简札。皆投其中。无不可者。日对翰墨。视为藏笥。则其体宜亦不能小也。遂样元白之诗筒而大其制焉。夫沙筒之为德。性温润色光洁。无刻镂雕琢之巧。又处安重而容受有量。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吾爱之。端在乎是。两弟皆曰此不独兄爱之。弟亦爱也。曹君乃命匠手成三筒。将各藏一焉。又俾余记其由。而道彦书其表。欲令异日子孙观者。知此筒之成。自吾三人者始也。耐斋集卷之四(南阳洪泰猷伯亨甫 著)
杂著
筑城议
耐斋集卷之四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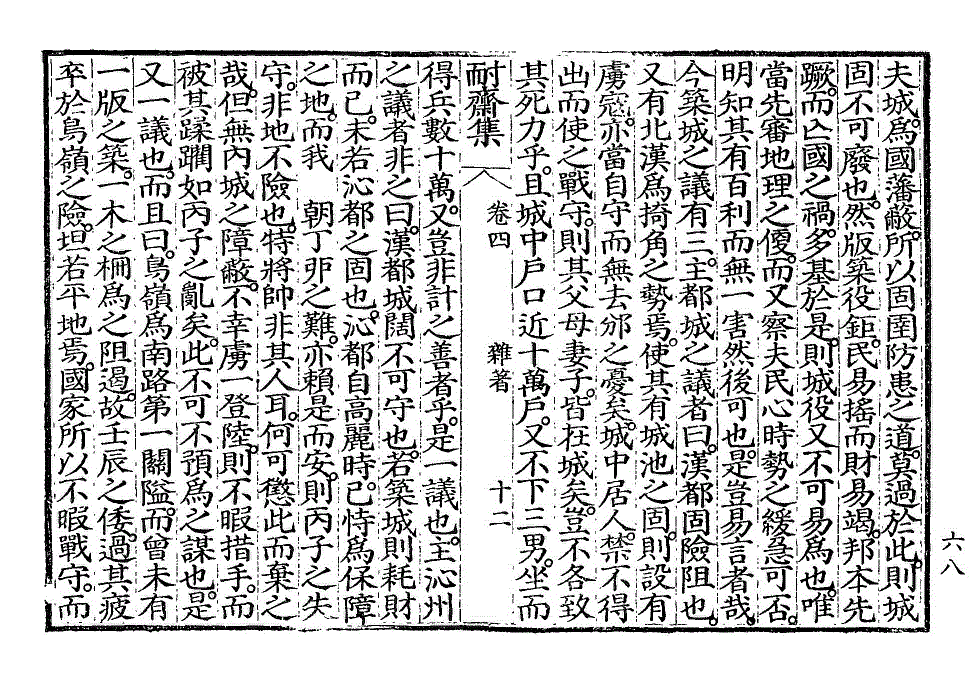 夫城。为国藩蔽。所以固圉防患之道。莫过于此。则城固不可废也。然版筑役钜。民易摇而财易竭。邦本先蹶。而亡国之祸。多基于是。则城役又不可易为也。唯当先审地理之便。而又察夫民心时势之缓急可否。明知其有百利而无一害然后可也。是岂易言者哉。今筑城之议有三。主都城之议者曰。汉都固险阻也。又有北汉为掎角之势焉。使其有城池之固。则设有虏寇。亦当自守而无去邠之忧矣。城中居人。禁不得出而使之战守。则其父母妻子。皆在城矣。岂不各致其死力乎。且城中户口近十万户。又不下三男。坐而得兵数十万。又岂非计之善者乎。是一议也。主沁州之议者非之曰。汉都城阔不可守也。若筑城则耗财而已。未若沁都之固也。沁都自高丽时。已恃为保障之地。而我 朝丁卯之难。亦赖是而安。则丙子之失守。非地不险也。特将帅非其人耳。何可惩此而弃之哉。但无内城之障蔽。不幸虏一登陆。则不暇措手。而被其蹂躏如丙子之乱矣。此不可不预为之谋也。是又一议也。而且曰。鸟岭为南路第一关隘。而曾未有一版之筑。一木之栅为之阻遏。故壬辰之倭。过其疲卒于鸟岭之险。坦若平地焉。国家所以不暇战守。而
夫城。为国藩蔽。所以固圉防患之道。莫过于此。则城固不可废也。然版筑役钜。民易摇而财易竭。邦本先蹶。而亡国之祸。多基于是。则城役又不可易为也。唯当先审地理之便。而又察夫民心时势之缓急可否。明知其有百利而无一害然后可也。是岂易言者哉。今筑城之议有三。主都城之议者曰。汉都固险阻也。又有北汉为掎角之势焉。使其有城池之固。则设有虏寇。亦当自守而无去邠之忧矣。城中居人。禁不得出而使之战守。则其父母妻子。皆在城矣。岂不各致其死力乎。且城中户口近十万户。又不下三男。坐而得兵数十万。又岂非计之善者乎。是一议也。主沁州之议者非之曰。汉都城阔不可守也。若筑城则耗财而已。未若沁都之固也。沁都自高丽时。已恃为保障之地。而我 朝丁卯之难。亦赖是而安。则丙子之失守。非地不险也。特将帅非其人耳。何可惩此而弃之哉。但无内城之障蔽。不幸虏一登陆。则不暇措手。而被其蹂躏如丙子之乱矣。此不可不预为之谋也。是又一议也。而且曰。鸟岭为南路第一关隘。而曾未有一版之筑。一木之栅为之阻遏。故壬辰之倭。过其疲卒于鸟岭之险。坦若平地焉。国家所以不暇战守。而耐斋集卷之四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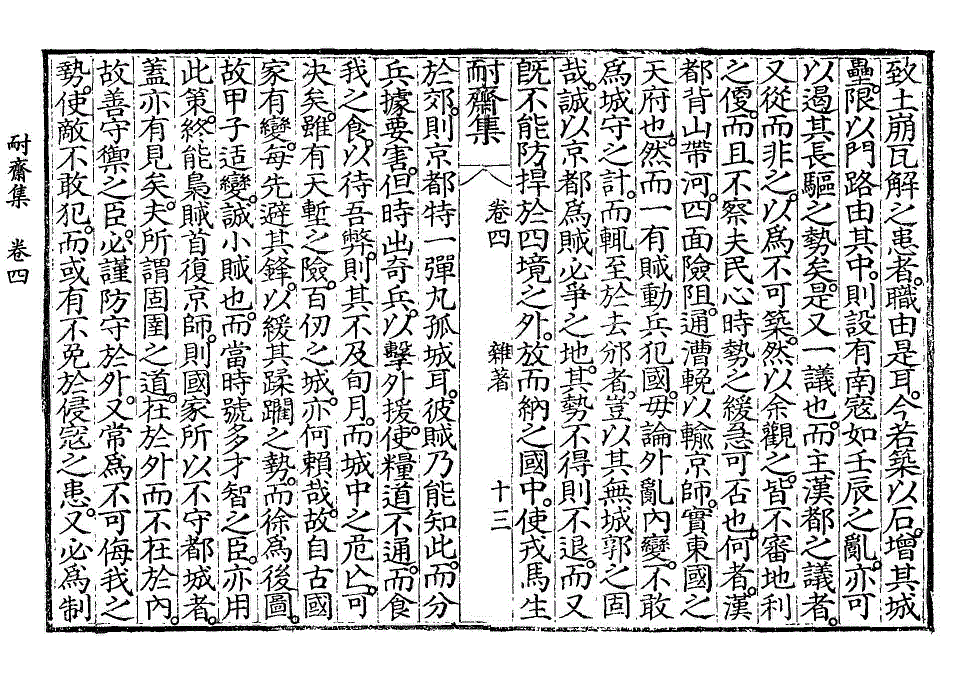 致土崩瓦解之患者。职由是耳。今若筑以石。增其城垒。限以门路由其中。则设有南寇如壬辰之乱。亦可以遏其长驱之势矣。是又一议也。而主汉都之议者。又从而非之。以为不可筑。然以余观之。皆不审地利之便。而且不察夫民心时势之缓急可否也。何者。汉都背山带河。四面险阻。通漕挽以输京师。实东国之天府也。然而一有贼动兵犯国。毋论外乱内变。不敢为城守之计。而辄至于去邠者。岂以其无城郭之固哉。诚以京都为贼必争之地。其势不得则不退。而又既不能防捍于四境之外。放而纳之国中。使戎马生于郊。则京都特一弹丸孤城耳。彼贼乃能知此。而分兵据要害。但时出奇兵。以击外援。使粮道不通。而食我之食。以待吾弊。则其不及旬月。而城中之危亡。可决矣。虽有天堑之险。百仞之城。亦何赖哉。故自古国家有变。每先避其锋。以缓其蹂躏之势。而徐为后图。故甲子适变。诚小贼也。而当时号多才智之臣。亦用此策。终能枭贼首复京师。则国家所以不守都城者。盖亦有见矣。夫所谓固圉之道。在于外而不在于内。故善守御之臣。必谨防守于外。又常为不可侮我之势。使敌不敢犯。而或有不免于侵寇之患。又必为制
致土崩瓦解之患者。职由是耳。今若筑以石。增其城垒。限以门路由其中。则设有南寇如壬辰之乱。亦可以遏其长驱之势矣。是又一议也。而主汉都之议者。又从而非之。以为不可筑。然以余观之。皆不审地利之便。而且不察夫民心时势之缓急可否也。何者。汉都背山带河。四面险阻。通漕挽以输京师。实东国之天府也。然而一有贼动兵犯国。毋论外乱内变。不敢为城守之计。而辄至于去邠者。岂以其无城郭之固哉。诚以京都为贼必争之地。其势不得则不退。而又既不能防捍于四境之外。放而纳之国中。使戎马生于郊。则京都特一弹丸孤城耳。彼贼乃能知此。而分兵据要害。但时出奇兵。以击外援。使粮道不通。而食我之食。以待吾弊。则其不及旬月。而城中之危亡。可决矣。虽有天堑之险。百仞之城。亦何赖哉。故自古国家有变。每先避其锋。以缓其蹂躏之势。而徐为后图。故甲子适变。诚小贼也。而当时号多才智之臣。亦用此策。终能枭贼首复京师。则国家所以不守都城者。盖亦有见矣。夫所谓固圉之道。在于外而不在于内。故善守御之臣。必谨防守于外。又常为不可侮我之势。使敌不敢犯。而或有不免于侵寇之患。又必为制耐斋集卷之四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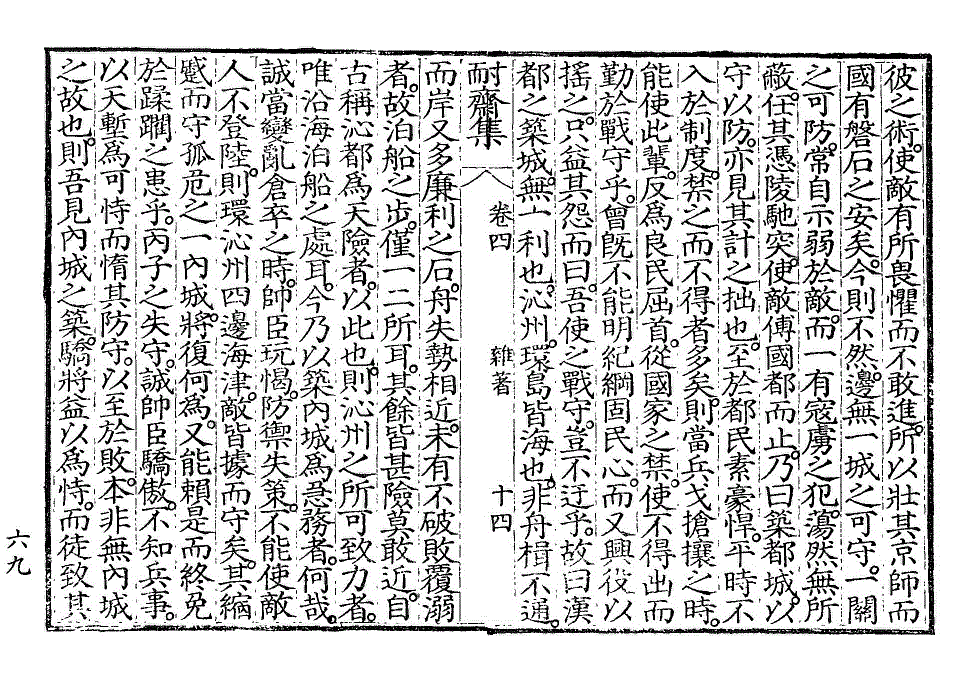 彼之术。使敌有所畏惧而不敢进。所以壮其京师而国有磐石之安矣。今则不然。边无一城之可守。一关之可防。常自示弱于敌。而一有寇虏之犯。荡然无所蔽。任其凭陵驰突。使敌傅国都而止。乃曰筑都城。以守以防。亦见其计之拙也。至于都民素豪悍。平时不入于制度。禁之而不得者多矣。则当兵戈抢攘之时。能使此辈。反为良民屈首。从国家之禁。使不得出而勤于战守乎。曾既不能明纪纲固民心。而又兴役以摇之。只益其怨而曰。吾使之战守。岂不迂乎。故曰汉都之筑城。无一利也。沁州。环岛皆海也。非舟楫不通。而岸又多廉利之石。舟失势相近。未有不破败覆溺者。故泊船之步。仅一二所耳。其馀皆甚险莫敢近。自古称沁都为天险者。以此也。则沁州之所可致力者。唯沿海泊船之处耳。今乃以筑内城为急务者。何哉。诚当变乱仓卒之时。帅臣玩愒。防御失策。不能使敌人不登陆。则环沁州四边海津。敌皆据而守矣。其缩蹙而守孤危之一内城。将复何为。又能赖是而终免于蹂躏之患乎。丙子之失守。诚帅臣骄傲。不知兵事。以天堑为可恃而惰其防守。以至于败。本非无内城之故也。则吾见内城之筑。骄将益以为恃。而徒致其
彼之术。使敌有所畏惧而不敢进。所以壮其京师而国有磐石之安矣。今则不然。边无一城之可守。一关之可防。常自示弱于敌。而一有寇虏之犯。荡然无所蔽。任其凭陵驰突。使敌傅国都而止。乃曰筑都城。以守以防。亦见其计之拙也。至于都民素豪悍。平时不入于制度。禁之而不得者多矣。则当兵戈抢攘之时。能使此辈。反为良民屈首。从国家之禁。使不得出而勤于战守乎。曾既不能明纪纲固民心。而又兴役以摇之。只益其怨而曰。吾使之战守。岂不迂乎。故曰汉都之筑城。无一利也。沁州。环岛皆海也。非舟楫不通。而岸又多廉利之石。舟失势相近。未有不破败覆溺者。故泊船之步。仅一二所耳。其馀皆甚险莫敢近。自古称沁都为天险者。以此也。则沁州之所可致力者。唯沿海泊船之处耳。今乃以筑内城为急务者。何哉。诚当变乱仓卒之时。帅臣玩愒。防御失策。不能使敌人不登陆。则环沁州四边海津。敌皆据而守矣。其缩蹙而守孤危之一内城。将复何为。又能赖是而终免于蹂躏之患乎。丙子之失守。诚帅臣骄傲。不知兵事。以天堑为可恃而惰其防守。以至于败。本非无内城之故也。则吾见内城之筑。骄将益以为恃。而徒致其耐斋集卷之四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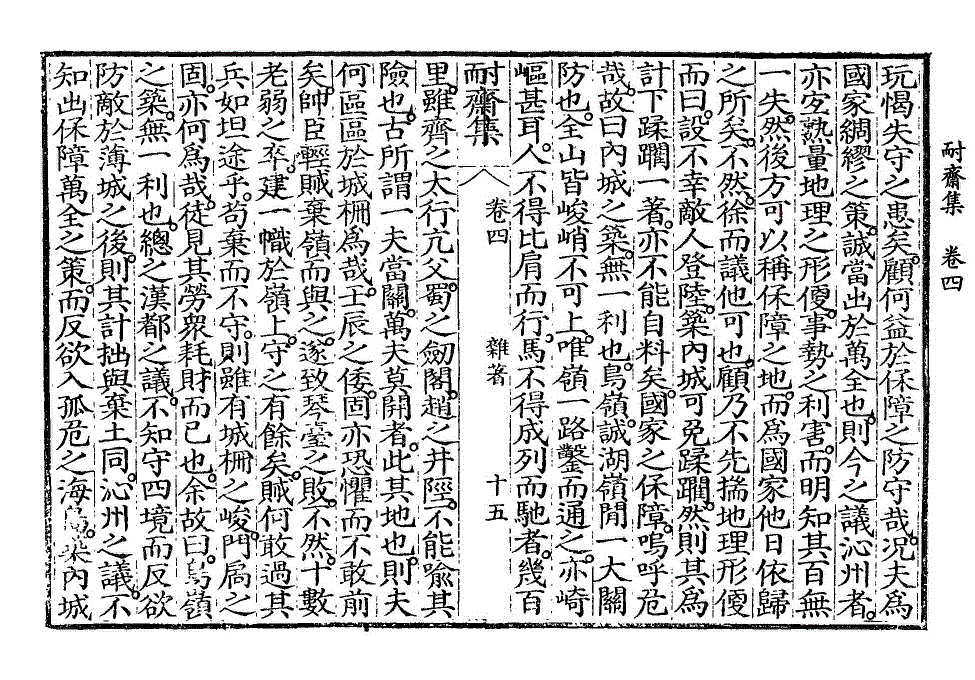 玩愒失守之患矣。顾何益于保障之防守哉。况夫为国家绸缪之策。诚当出于万全也。则今之议沁州者。亦宜熟量地理之形便。事势之利害。而明知其百无一失。然后方可以称保障之地。而为国家他日依归之所矣。不然。徐而议他可也。顾乃不先揣地理形便而曰。设不幸敌人登陆。筑内城可免蹂躏。然则其为计下蹂躏一著。亦不能自料矣。国家之保障。呜呼危哉。故曰内城之筑。无一利也。鸟岭。诚湖岭间一大关防也。全山皆峻峭不可上。唯岭一路凿而通之。亦崎岖甚耳。人不得比肩而行。马不得成列而驰者。几百里。虽齐之太行亢父。蜀之剑阁。赵之井陉。不能喻其险也。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者。此其地也。则夫何区区于城栅为哉。壬辰之倭。固亦恐惧而不敢前矣。帅臣轻贼弃岭而与之。遂致琴台之败。不然。十数老弱之卒。建一帜于岭上。守之有馀矣。贼何敢过其兵如坦途乎。苟弃而不守。则虽有城栅之峻。门扃之固。亦何为哉。徒见其劳众耗财而已也。余故曰。鸟岭之筑。无一利也。总之汉都之议。不知守四境而反欲防敌于薄城之后。则其计拙与弃土同。沁州之议。不知出保障万全之策。而反欲入孤危之海岛。筑内城
玩愒失守之患矣。顾何益于保障之防守哉。况夫为国家绸缪之策。诚当出于万全也。则今之议沁州者。亦宜熟量地理之形便。事势之利害。而明知其百无一失。然后方可以称保障之地。而为国家他日依归之所矣。不然。徐而议他可也。顾乃不先揣地理形便而曰。设不幸敌人登陆。筑内城可免蹂躏。然则其为计下蹂躏一著。亦不能自料矣。国家之保障。呜呼危哉。故曰内城之筑。无一利也。鸟岭。诚湖岭间一大关防也。全山皆峻峭不可上。唯岭一路凿而通之。亦崎岖甚耳。人不得比肩而行。马不得成列而驰者。几百里。虽齐之太行亢父。蜀之剑阁。赵之井陉。不能喻其险也。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者。此其地也。则夫何区区于城栅为哉。壬辰之倭。固亦恐惧而不敢前矣。帅臣轻贼弃岭而与之。遂致琴台之败。不然。十数老弱之卒。建一帜于岭上。守之有馀矣。贼何敢过其兵如坦途乎。苟弃而不守。则虽有城栅之峻。门扃之固。亦何为哉。徒见其劳众耗财而已也。余故曰。鸟岭之筑。无一利也。总之汉都之议。不知守四境而反欲防敌于薄城之后。则其计拙与弃土同。沁州之议。不知出保障万全之策。而反欲入孤危之海岛。筑内城耐斋集卷之四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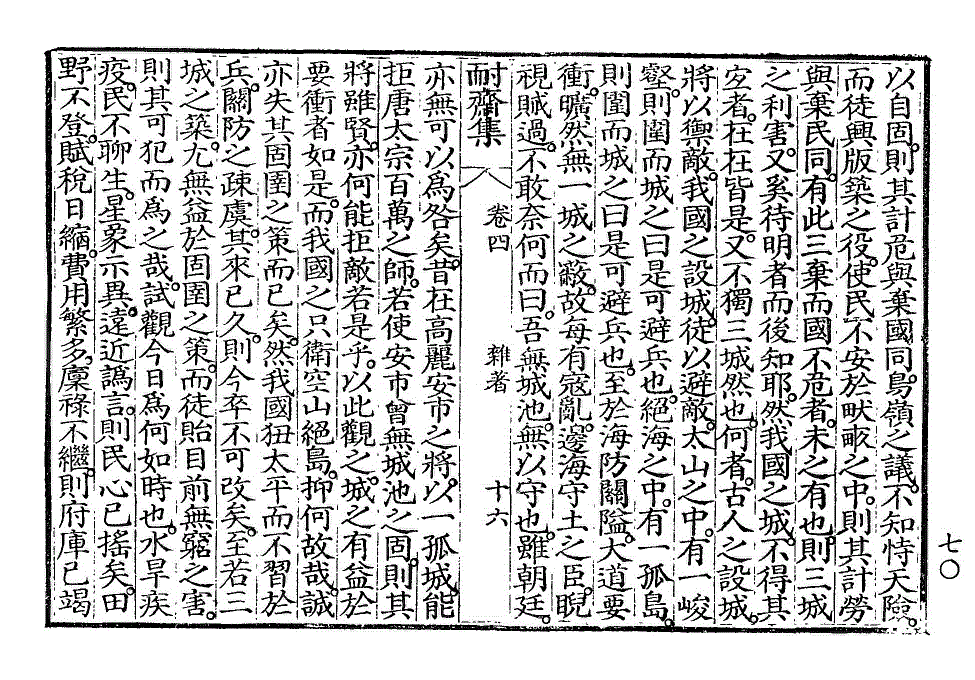 以自固。则其计危与弃国同。鸟岭之议。不知恃天险。而徒兴版筑之役。使民不安于畎亩之中。则其计劳与弃民同。有此三弃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则三城之利害。又奚待明者而后知耶。然我国之城。不得其宜者。在在皆是。又不独三城然也。何者。古人之设城。将以御敌。我国之设城。徒以避敌。太山之中。有一峻壑。则围而城之曰是可避兵也。绝海之中。有一孤岛。则围而城之曰是可避兵也。至于海防关隘。大道要冲。旷然无一城之蔽。故每有寇乱。边海守土之臣。睨视贼过。不敢奈何而曰。吾无城池。无以守也。虽朝廷。亦无可以为咎矣。昔在高丽安韨之将。以一孤城。能拒唐太宗百万之师。若使安韨曾无城池之固。则其将虽贤。亦何能拒敌若是乎。以此观之。城之有益于要冲者如是。而我国之只卫空山绝岛。抑何故哉。诚亦失其固圉之策而已矣。然我国狃太平而不习于兵。关防之疏虞。其来已久。则今卒不可改矣。至若三城之筑。尤无益于固圉之策。而徒贻目前无穷之害。则其可犯而为之哉。试观今日为何如时也。水旱疾疫。民不聊生。星象示异。远近讹言。则民心已摇矣。田野不登。赋税日缩。费用繁多。廪禄不继。则府库已竭
以自固。则其计危与弃国同。鸟岭之议。不知恃天险。而徒兴版筑之役。使民不安于畎亩之中。则其计劳与弃民同。有此三弃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则三城之利害。又奚待明者而后知耶。然我国之城。不得其宜者。在在皆是。又不独三城然也。何者。古人之设城。将以御敌。我国之设城。徒以避敌。太山之中。有一峻壑。则围而城之曰是可避兵也。绝海之中。有一孤岛。则围而城之曰是可避兵也。至于海防关隘。大道要冲。旷然无一城之蔽。故每有寇乱。边海守土之臣。睨视贼过。不敢奈何而曰。吾无城池。无以守也。虽朝廷。亦无可以为咎矣。昔在高丽安韨之将。以一孤城。能拒唐太宗百万之师。若使安韨曾无城池之固。则其将虽贤。亦何能拒敌若是乎。以此观之。城之有益于要冲者如是。而我国之只卫空山绝岛。抑何故哉。诚亦失其固圉之策而已矣。然我国狃太平而不习于兵。关防之疏虞。其来已久。则今卒不可改矣。至若三城之筑。尤无益于固圉之策。而徒贻目前无穷之害。则其可犯而为之哉。试观今日为何如时也。水旱疾疫。民不聊生。星象示异。远近讹言。则民心已摇矣。田野不登。赋税日缩。费用繁多。廪禄不继。则府库已竭耐斋集卷之四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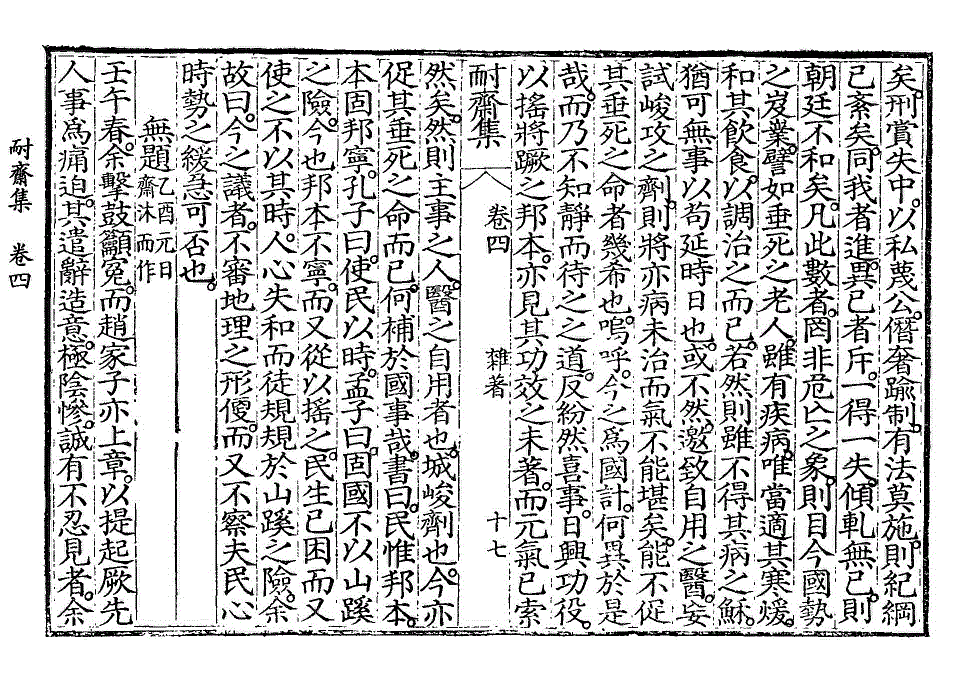 矣。刑赏失中。以私蔑公。僭奢踰制。有法莫施。则纪纲已紊矣。同我者进。异己者斥。一得一失。倾轧无已。则朝廷不和矣。凡此数者。罔非危亡之象。则目今国势之岌嶪。譬如垂死之老人。虽有疾病。唯当适其寒煖。和其饮食。以调治之而已。若然则虽不得其病之稣。犹可无事以苟延时日也。或不然。邀致自用之医。妄试峻攻之剂。则将亦病未治而气不能堪矣。能不促其垂死之命者几希也。呜呼。今之为国计。何异于是哉。而乃不知静而待之之道。反纷然喜事。日兴功役。以摇将蹶之邦本。亦见其功效之未著。而元气已索然矣。然则主事之人。医之自用者也。城峻剂也。今亦促其垂死之命而已。何补于国事哉。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曰。固国不以山蹊之险。今也邦本不宁。而又从以摇之。民生已困而又使之不以其时。人心失和而徒规规于山蹊之险。余故曰。今之议者。不审地理之形便。而又不察夫民心时势之缓急可否也。
矣。刑赏失中。以私蔑公。僭奢踰制。有法莫施。则纪纲已紊矣。同我者进。异己者斥。一得一失。倾轧无已。则朝廷不和矣。凡此数者。罔非危亡之象。则目今国势之岌嶪。譬如垂死之老人。虽有疾病。唯当适其寒煖。和其饮食。以调治之而已。若然则虽不得其病之稣。犹可无事以苟延时日也。或不然。邀致自用之医。妄试峻攻之剂。则将亦病未治而气不能堪矣。能不促其垂死之命者几希也。呜呼。今之为国计。何异于是哉。而乃不知静而待之之道。反纷然喜事。日兴功役。以摇将蹶之邦本。亦见其功效之未著。而元气已索然矣。然则主事之人。医之自用者也。城峻剂也。今亦促其垂死之命而已。何补于国事哉。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曰。固国不以山蹊之险。今也邦本不宁。而又从以摇之。民生已困而又使之不以其时。人心失和而徒规规于山蹊之险。余故曰。今之议者。不审地理之形便。而又不察夫民心时势之缓急可否也。无题(乙酉元日斋沐而作)
壬午春。余击鼓吁冤。而赵家子亦上章。以提起厥先人事为痛迫。其遣辞造意。极阴惨。诚有不忍见者。余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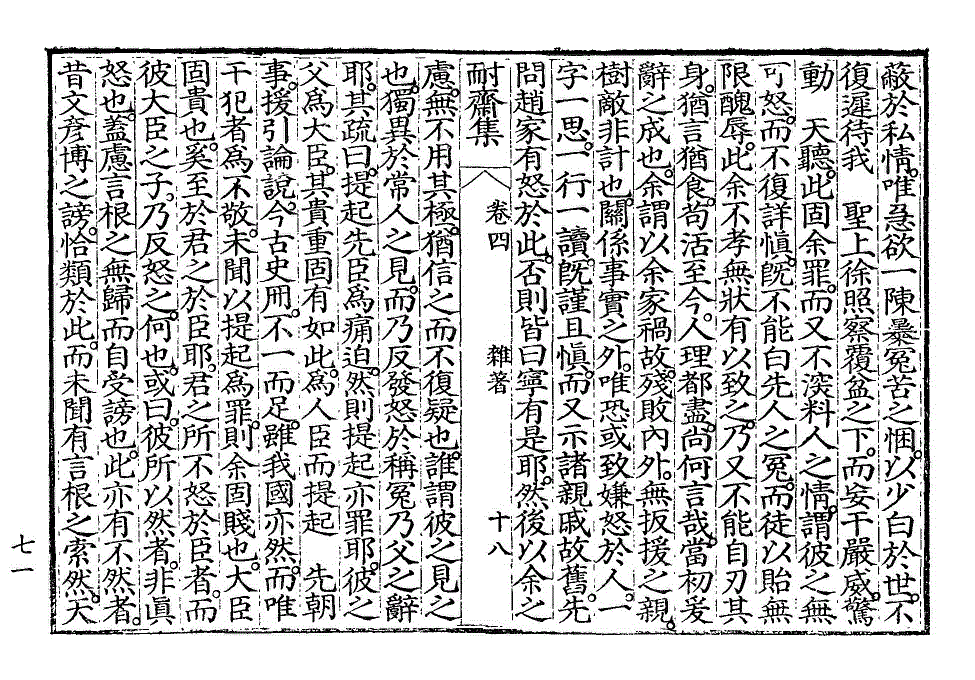 蔽于私情。唯急欲一陈㬥冤苦之悃。以少白于世。不复迟待我 圣上徐照察覆盆之下。而妄干严威。惊动 天听。此固余罪。而又不深料人之情。谓彼之无可怒。而不复详慎。既不能白先人之冤。而徒以贻无限丑辱。此余不孝无状有以致之。乃又不能自刃其身。犹言犹食。苟活至今。人理都尽。尚何言哉。当初爰辞之成也。余谓以余家祸故。残败内外。无扳援之亲。树敌非计也。关系事实之外。唯恐或致嫌怒于人。一字一思。一行一读。既谨且慎。而又示诸亲戚故旧。先问赵家有怒于此。否则皆曰宁有是耶。然后以余之虑。无不用其极。犹信之而不复疑也。谁谓彼之见之也。独异于常人之见。而乃反发怒于称冤乃父之辞耶。其疏曰。提起先臣为痛迫。然则提起亦罪耶。彼之父为大臣。其贵重固有如此。为人臣而提起 先朝事。援引论说。今古史册。不一而足。虽我国亦然。而唯干犯者为不敬。未闻以提起为罪。则余固贱也。大臣固贵也。奚至于君之于臣耶。君之所不怒于臣者。而彼大臣之子。乃反怒之。何也。或曰。彼所以然者。非真怒也。盖虑言根之无归而自受谤也。此亦有不然者。昔文彦博之谤。恰类于此。而未闻有言根之索然。天
蔽于私情。唯急欲一陈㬥冤苦之悃。以少白于世。不复迟待我 圣上徐照察覆盆之下。而妄干严威。惊动 天听。此固余罪。而又不深料人之情。谓彼之无可怒。而不复详慎。既不能白先人之冤。而徒以贻无限丑辱。此余不孝无状有以致之。乃又不能自刃其身。犹言犹食。苟活至今。人理都尽。尚何言哉。当初爰辞之成也。余谓以余家祸故。残败内外。无扳援之亲。树敌非计也。关系事实之外。唯恐或致嫌怒于人。一字一思。一行一读。既谨且慎。而又示诸亲戚故旧。先问赵家有怒于此。否则皆曰宁有是耶。然后以余之虑。无不用其极。犹信之而不复疑也。谁谓彼之见之也。独异于常人之见。而乃反发怒于称冤乃父之辞耶。其疏曰。提起先臣为痛迫。然则提起亦罪耶。彼之父为大臣。其贵重固有如此。为人臣而提起 先朝事。援引论说。今古史册。不一而足。虽我国亦然。而唯干犯者为不敬。未闻以提起为罪。则余固贱也。大臣固贵也。奚至于君之于臣耶。君之所不怒于臣者。而彼大臣之子。乃反怒之。何也。或曰。彼所以然者。非真怒也。盖虑言根之无归而自受谤也。此亦有不然者。昔文彦博之谤。恰类于此。而未闻有言根之索然。天耐斋集卷之四 第 72H 页
 下后世。何尝有以此谤疑潞公者耶。然则彼大臣之子。待乃父如潞公足矣。今乃欲胜潞公。而反唯言根之务如此。岂真胜潞公耶。且余之爰辞。自白吾冤而已。言根尚有所归。则不可谓无言根也。彼必欲舍彼而取此。抑何也。岂以言根事系宫禁。而余家又戚联宫掖。故尤致疑于造谤。而唯恐或脱耶。然则余惑滋甚。今有二焉。一自谓无嫌怨而联宫掖。一自谓有嫌怨而非联宫掖。将使言根出于无嫌怨而联宫掖者之口。则人之听者。将谓之造言耶。抑谓之实言耶。使言根出于有嫌怨而非联宫掖者之口。则人之听者将谓之实言耶。抑谓之造言耶。此则虽妇孺儿童。一听可卞。而独彼之操持吾家。或恐不力。挤之罔测落井而又下石。抑又何故。实未可知也。呜呼。彼与我为父之情。均各自为父也。宜其不顾籍于人。若推其父吾父之心。以及于人。则无所相害于为父。而反怒人之为父者。此岂常情所到耶。人于天地间。惟君与父而已。欲白父冤而先欺其君。则是何异慢天而祈福。若无人祸。必有天殃矣。设令无是而巧售欺诬之计。抑必羞死父之颜于泉下也。何敢谓白父之冤耶。未知向者彼与我之言。谁虚谁实。谁白直谁妆撰。世惟
下后世。何尝有以此谤疑潞公者耶。然则彼大臣之子。待乃父如潞公足矣。今乃欲胜潞公。而反唯言根之务如此。岂真胜潞公耶。且余之爰辞。自白吾冤而已。言根尚有所归。则不可谓无言根也。彼必欲舍彼而取此。抑何也。岂以言根事系宫禁。而余家又戚联宫掖。故尤致疑于造谤。而唯恐或脱耶。然则余惑滋甚。今有二焉。一自谓无嫌怨而联宫掖。一自谓有嫌怨而非联宫掖。将使言根出于无嫌怨而联宫掖者之口。则人之听者。将谓之造言耶。抑谓之实言耶。使言根出于有嫌怨而非联宫掖者之口。则人之听者将谓之实言耶。抑谓之造言耶。此则虽妇孺儿童。一听可卞。而独彼之操持吾家。或恐不力。挤之罔测落井而又下石。抑又何故。实未可知也。呜呼。彼与我为父之情。均各自为父也。宜其不顾籍于人。若推其父吾父之心。以及于人。则无所相害于为父。而反怒人之为父者。此岂常情所到耶。人于天地间。惟君与父而已。欲白父冤而先欺其君。则是何异慢天而祈福。若无人祸。必有天殃矣。设令无是而巧售欺诬之计。抑必羞死父之颜于泉下也。何敢谓白父之冤耶。未知向者彼与我之言。谁虚谁实。谁白直谁妆撰。世惟耐斋集卷之四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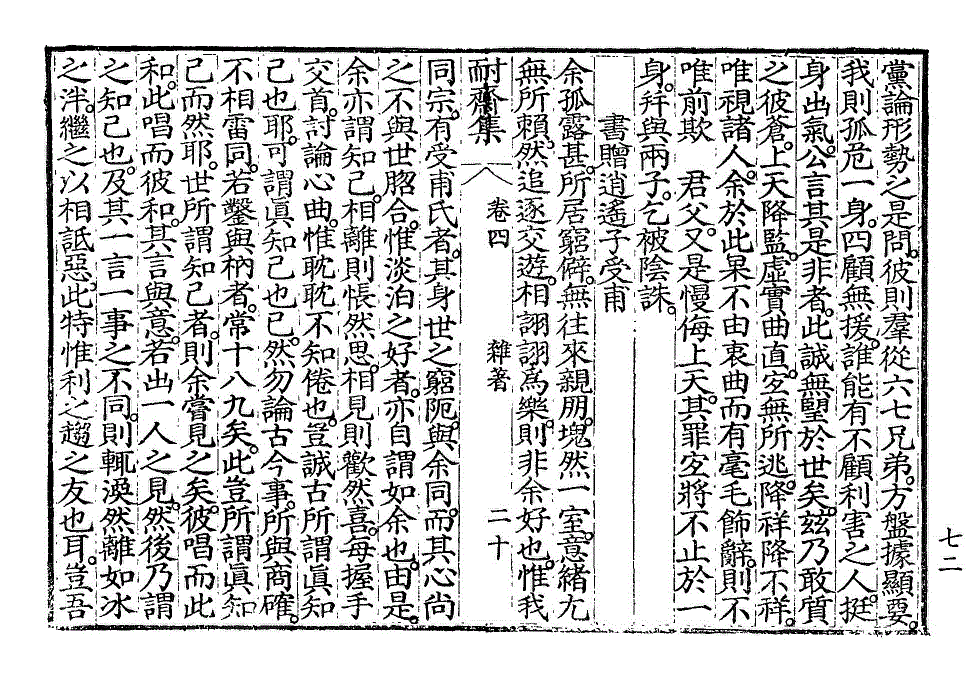 党论形势之是问。彼则群从六七兄弟。方盘据显要。我则孤危一身。四顾无援。谁能有不顾利害之人。挺身出气。公言其是非者。此诚无望于世矣。玆乃敢质之彼苍。上天降监。虚实曲直。宜无所逃。降祥降不祥。唯视诸人。余于此果不由衷曲而有毫毛饰辞。则不唯前欺 君父。又是慢侮上天。其罪宜将不止于一身。并与两子。乞被阴诛。
党论形势之是问。彼则群从六七兄弟。方盘据显要。我则孤危一身。四顾无援。谁能有不顾利害之人。挺身出气。公言其是非者。此诚无望于世矣。玆乃敢质之彼苍。上天降监。虚实曲直。宜无所逃。降祥降不祥。唯视诸人。余于此果不由衷曲而有毫毛饰辞。则不唯前欺 君父。又是慢侮上天。其罪宜将不止于一身。并与两子。乞被阴诛。书赠逍遥子受甫
余孤露甚。所居穷僻。无往来亲朋。块然一室。意绪尤无所赖。然追逐交游。相诩诩为乐。则非余好也。惟我同宗。有受甫氏者。其身世之穷阨。与余同。而其心尚之不与世吻合。惟淡泊之好者。亦自谓如余也。由是。余亦谓知己。相离则怅然思。相见则欢然喜。每握手交首。讨论心曲。惟耽耽不知倦也。岂诚古所谓真知己也耶。可谓真知己也已。然勿论古今事。所与商确。不相雷同。若凿与枘者。常十八九矣。此岂所谓真知己而然耶。世所谓知己者。则余尝见之矣。彼唱而此和。此唱而彼和。其言与意。若出一人之见。然后乃谓之知己也。及其一言一事之不同。则辄涣然离如冰之泮。继之以相诋恶。此特惟利之趋之友也耳。岂吾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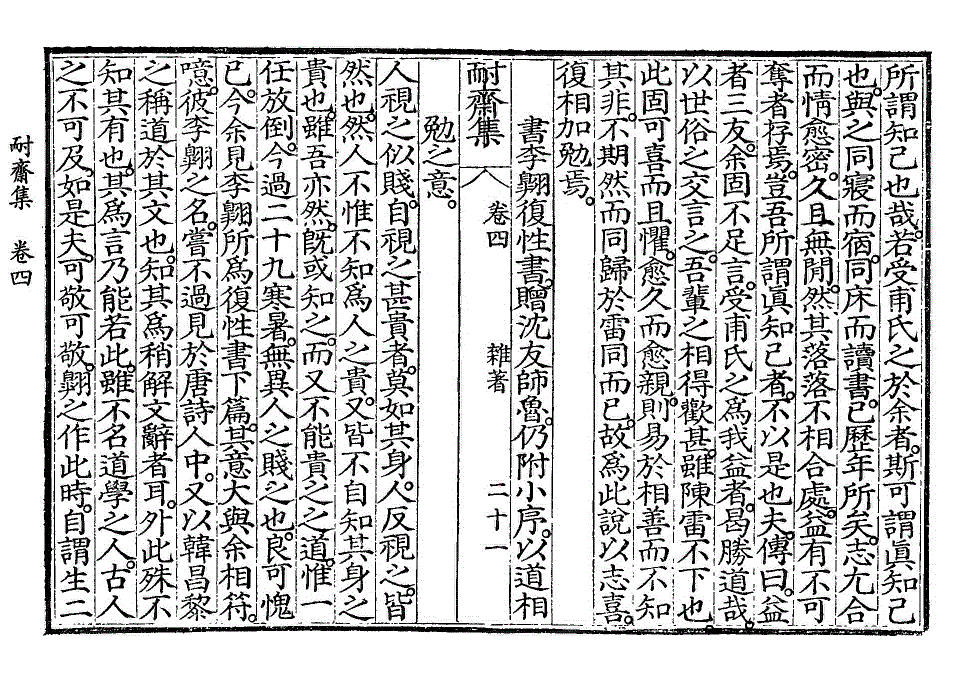 所谓知己也哉。若受甫氏之于余者。斯可谓真知己也。与之同寝而宿。同床而读书。已历年所矣。志尤合而情愈密。久且无间。然其落落不相合处。益有不可夺者存焉。岂吾所谓真知己者。不以是也夫。传曰。益者三友。余固不足言。受甫氏之为我益者。曷胜道哉。以世俗之交言之。吾辈之相得欢甚。虽陈雷不下也。此固可喜而且惧。愈久而愈亲。则易于相善而不知其非。不期然而同归于雷同而已。故为此说以志喜。复相加勉焉。
所谓知己也哉。若受甫氏之于余者。斯可谓真知己也。与之同寝而宿。同床而读书。已历年所矣。志尤合而情愈密。久且无间。然其落落不相合处。益有不可夺者存焉。岂吾所谓真知己者。不以是也夫。传曰。益者三友。余固不足言。受甫氏之为我益者。曷胜道哉。以世俗之交言之。吾辈之相得欢甚。虽陈雷不下也。此固可喜而且惧。愈久而愈亲。则易于相善而不知其非。不期然而同归于雷同而已。故为此说以志喜。复相加勉焉。书李翱复性书。赠沈友师鲁。仍附小序。以道相勉之意。
人视之似贱。自视之甚贵者。莫如其身。人反视之。皆然也。然人不惟不知为人之贵。又皆不自知其身之贵也。虽吾亦然。既或知之。而又不能贵之之道。惟一任放倒。今过二十九寒暑。无异人之贱之也。良可愧已。今余见李翱所为复性书下篇。其意大与余相符。噫。彼李翱之名。尝不过见于唐诗人中。又以韩昌黎之称道于其文也。知其为稍解文辞者耳。外此殊不知其有也。其为言乃能若此。虽不名道学之人。古人之不可及。如是夫。可敬可敬。翱之作此时。自谓生二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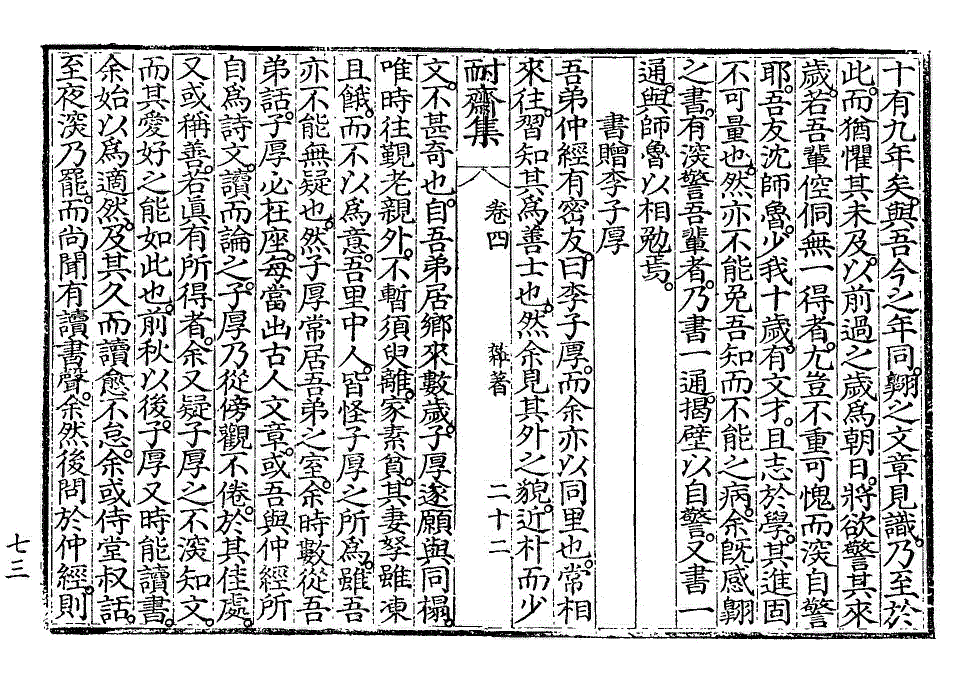 十有九年矣。与吾今之年同。翱之文章见识。乃至于此。而犹惧其未及。以前过之岁为朝日。将欲警其来岁。若吾辈倥侗无一得者。尤岂不重可愧而深自警耶。吾友沈师鲁。少我十岁。有文才。且志于学。其进固不可量也。然亦不能免吾知而不能之病。余既感翱之书。有深警吾辈者。乃书一通。揭壁以自警。又书一通。与师鲁以相勉焉。
十有九年矣。与吾今之年同。翱之文章见识。乃至于此。而犹惧其未及。以前过之岁为朝日。将欲警其来岁。若吾辈倥侗无一得者。尤岂不重可愧而深自警耶。吾友沈师鲁。少我十岁。有文才。且志于学。其进固不可量也。然亦不能免吾知而不能之病。余既感翱之书。有深警吾辈者。乃书一通。揭壁以自警。又书一通。与师鲁以相勉焉。书赠李子厚
吾弟仲经有密友。曰李子厚。而余亦以同里也。常相来往。习知其为善士也。然余见其外之貌。近朴而少文。不甚奇也。自吾弟居乡来数岁。子厚遂愿与同榻。唯时往觐老亲外。不暂须臾离。家素贫。其妻孥虽冻且饿。而不以为意。吾里中人。皆怪子厚之所为。虽吾亦不能无疑也。然子厚常居吾弟之室。余时数从吾弟话。子厚必在座。每当出古人文章。或吾与仲经所自为诗文。读而论之。子厚乃从傍观不倦。于其佳处。又或称善。若真有所得者。余又疑子厚之不深知文。而其爱好之能如此也。前秋以后。子厚又时能读书。余始以为适然。及其久而读愈不怠。余或侍堂叔话。至夜深乃罢。而尚闻有读书声。余然后问于仲经。则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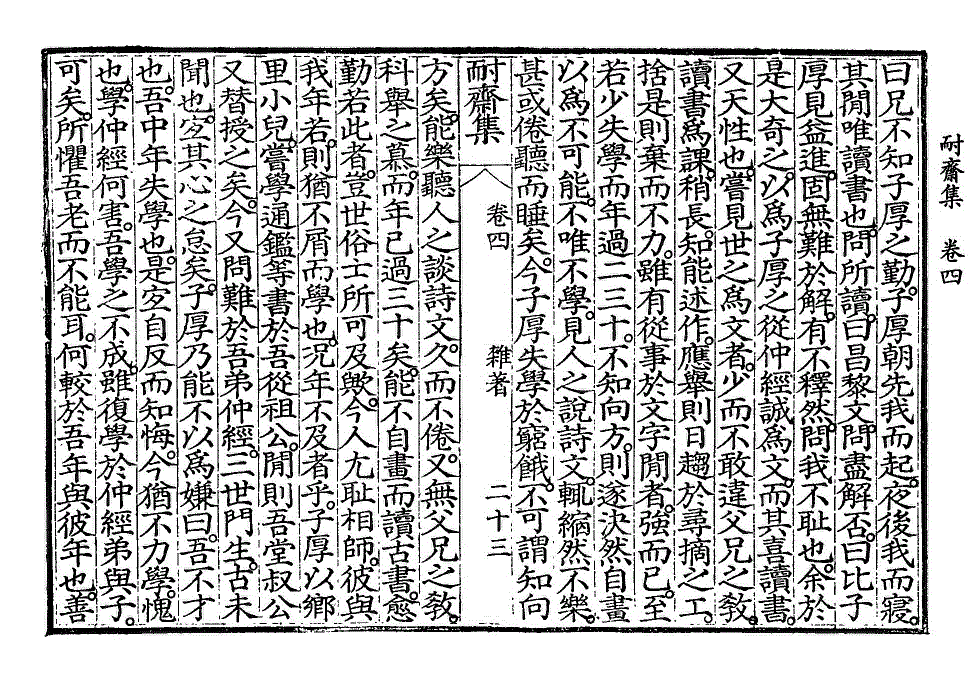 曰兄不知子厚之勤。子厚朝先我而起。夜后我而寝。其间唯读书也。问所读。曰昌黎文。问尽解否。曰比子厚见益进。固无难于解。有不释然。问我不耻也。余于是大奇之。以为子厚之从仲经诚为文。而其喜读书。又天性也。尝见世之为文者。少而不敢违父兄之教。读书为课。稍长。知能述作。应举则日趋于寻摘之工。舍是则弃而不力。虽有从事于文字间者。强而已。至若少失学而年过二三十。不知向方。则遂决然自画以为不可能。不唯不学。见人之说诗文。辄缩然不乐。甚或倦听而睡矣。今子厚失学于穷饿。不可谓知向方矣。能乐听人之谈诗文。久而不倦。又无父兄之教。科举之慕。而年已过三十矣。能不自画而读古书。愈勤若此者。岂世俗士所可及欤。今人尤耻相师。彼与我年若。则犹不屑而学也。况年不及者乎。子厚以乡里小儿。尝学通鉴等书于吾从祖公。间则吾堂叔公又替授之矣。今又问难于吾弟仲经。三世门生。古未闻也。宜其心之怠矣。子厚乃能不以为嫌曰。吾不才也。吾中年失学也。是宜自反而知悔。今犹不力学。愧也。学仲经何害。吾学之不成。虽复学于仲经弟与子。可矣。所惧吾老而不能耳。何较于吾年与彼年也。善
曰兄不知子厚之勤。子厚朝先我而起。夜后我而寝。其间唯读书也。问所读。曰昌黎文。问尽解否。曰比子厚见益进。固无难于解。有不释然。问我不耻也。余于是大奇之。以为子厚之从仲经诚为文。而其喜读书。又天性也。尝见世之为文者。少而不敢违父兄之教。读书为课。稍长。知能述作。应举则日趋于寻摘之工。舍是则弃而不力。虽有从事于文字间者。强而已。至若少失学而年过二三十。不知向方。则遂决然自画以为不可能。不唯不学。见人之说诗文。辄缩然不乐。甚或倦听而睡矣。今子厚失学于穷饿。不可谓知向方矣。能乐听人之谈诗文。久而不倦。又无父兄之教。科举之慕。而年已过三十矣。能不自画而读古书。愈勤若此者。岂世俗士所可及欤。今人尤耻相师。彼与我年若。则犹不屑而学也。况年不及者乎。子厚以乡里小儿。尝学通鉴等书于吾从祖公。间则吾堂叔公又替授之矣。今又问难于吾弟仲经。三世门生。古未闻也。宜其心之怠矣。子厚乃能不以为嫌曰。吾不才也。吾中年失学也。是宜自反而知悔。今犹不力学。愧也。学仲经何害。吾学之不成。虽复学于仲经弟与子。可矣。所惧吾老而不能耳。何较于吾年与彼年也。善耐斋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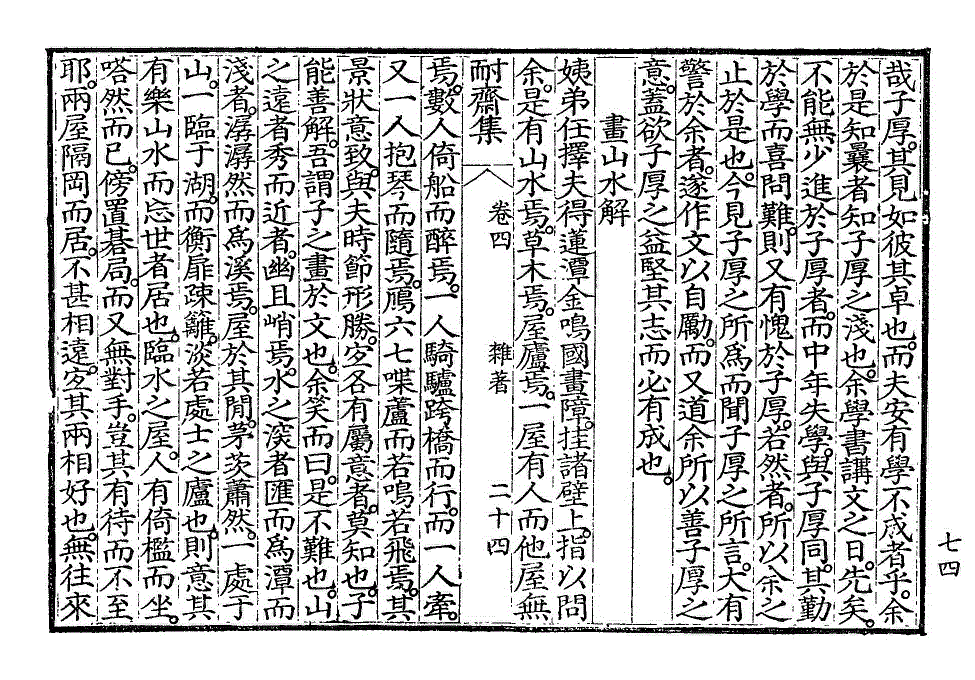 哉子厚。其见如彼其卓也。而夫安有学不成者乎。余于是知曩者知子厚之浅也。余学书讲文之日。先矣。不能无少进于子厚者。而中年失学。与子厚同。其勤于学而喜问难。则又有愧于子厚。若然者。所以余之止于是也。今见子厚之所为而闻子厚之所言。大有警于余者。遂作文以自励。而又道余所以善子厚之意。盖欲子厚之益坚其志而必有成也。
哉子厚。其见如彼其卓也。而夫安有学不成者乎。余于是知曩者知子厚之浅也。余学书讲文之日。先矣。不能无少进于子厚者。而中年失学。与子厚同。其勤于学而喜问难。则又有愧于子厚。若然者。所以余之止于是也。今见子厚之所为而闻子厚之所言。大有警于余者。遂作文以自励。而又道余所以善子厚之意。盖欲子厚之益坚其志而必有成也。画山水解
姨弟任择夫得莲潭金鸣国画障。挂诸壁上。指以问余。是有山水焉。草木焉。屋庐焉。一屋有人而他屋无焉。数人倚船而醉焉。一人骑驴跨桥而行。而一人牵。又一人抱琴而随焉。雁六七喋芦而若鸣若飞焉。其景状意致。与夫时节形胜。宜各有属意者。莫知也。子能善解。吾谓子之画于文也。余笑而曰。是不难也。山之远者秀而近者。幽且峭焉。水之深者汇而为潭而浅者。潺潺然而为溪焉。屋于其间。茅茨萧然。一处于山。一临于湖。而衡扉疏篱。淡若处士之庐也。则意其有乐山水而忘世者居也。临水之屋。人有倚槛而坐。嗒然而已。傍置棋局。而又无对手。岂其有待而不至耶。两屋隔冈而居。不甚相远。宜其两相好也。无往来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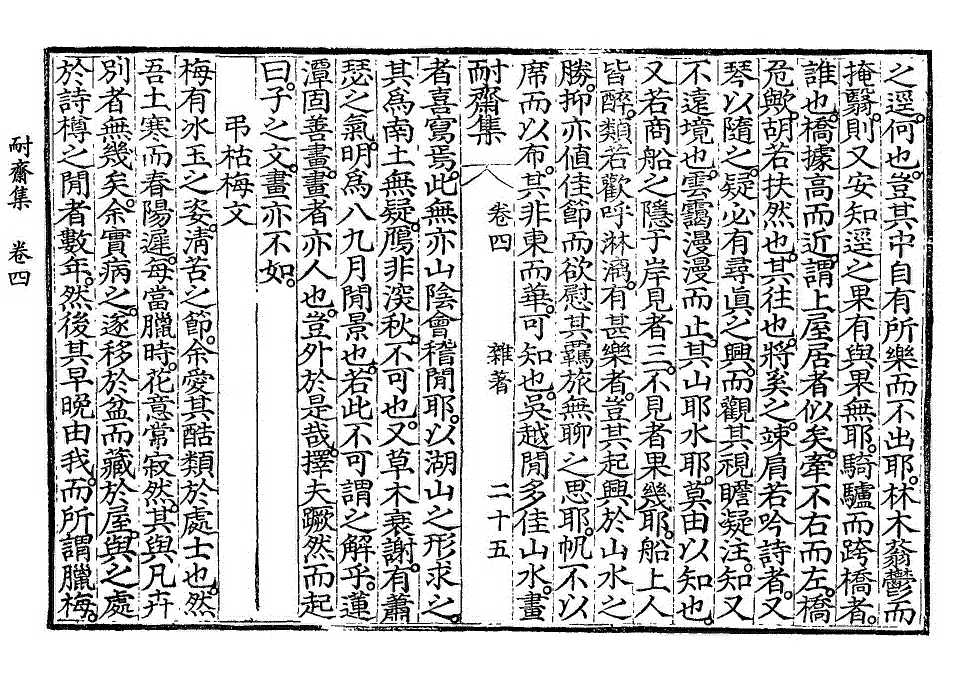 之径。何也。岂其中自有所乐而不出耶。林木蓊郁而掩翳。则又安知径之果有与果无耶。骑驴而跨桥者。谁也。桥据高而近。谓上屋居者似矣。牵不右而左。桥危欤。胡若扶然也。其往也。将奚之。竦肩若吟诗者。又琴以随之。疑必有寻真之兴。而观其视瞻凝注。知又不远境也。云霭漫漫而止。其山耶水耶。莫由以知也。又若商船之隐于岸见者三。不见者果几耶。船上人皆醉。类若欢呼淋漓。有甚乐者。岂其起兴于山水之胜。抑亦值佳节而欲慰其羁旅无聊之思耶。帆不以席而以布。其非东而华。可知也。吴越间多佳山水。画者喜写焉。此无亦山阴会稽间耶。以湖山之形求之。其为南土无疑。雁非深秋。不可也。又草木衰谢。有萧瑟之气。明为八九月间景也。若此不可谓之解乎。莲潭固善画。画者亦人也。岂外于是哉。择夫蹶然而起曰。子之文。画亦不如。
之径。何也。岂其中自有所乐而不出耶。林木蓊郁而掩翳。则又安知径之果有与果无耶。骑驴而跨桥者。谁也。桥据高而近。谓上屋居者似矣。牵不右而左。桥危欤。胡若扶然也。其往也。将奚之。竦肩若吟诗者。又琴以随之。疑必有寻真之兴。而观其视瞻凝注。知又不远境也。云霭漫漫而止。其山耶水耶。莫由以知也。又若商船之隐于岸见者三。不见者果几耶。船上人皆醉。类若欢呼淋漓。有甚乐者。岂其起兴于山水之胜。抑亦值佳节而欲慰其羁旅无聊之思耶。帆不以席而以布。其非东而华。可知也。吴越间多佳山水。画者喜写焉。此无亦山阴会稽间耶。以湖山之形求之。其为南土无疑。雁非深秋。不可也。又草木衰谢。有萧瑟之气。明为八九月间景也。若此不可谓之解乎。莲潭固善画。画者亦人也。岂外于是哉。择夫蹶然而起曰。子之文。画亦不如。吊枯梅文
梅有冰玉之姿。清苦之节。余爱其酷类于处士也。然吾土寒而春阳迟。每当腊时。花意常寂然。其与凡卉别者无几矣。余实病之。遂移于盆而藏于屋。与之处于诗樽之间者数年。然后其早晚由我。而所谓腊梅。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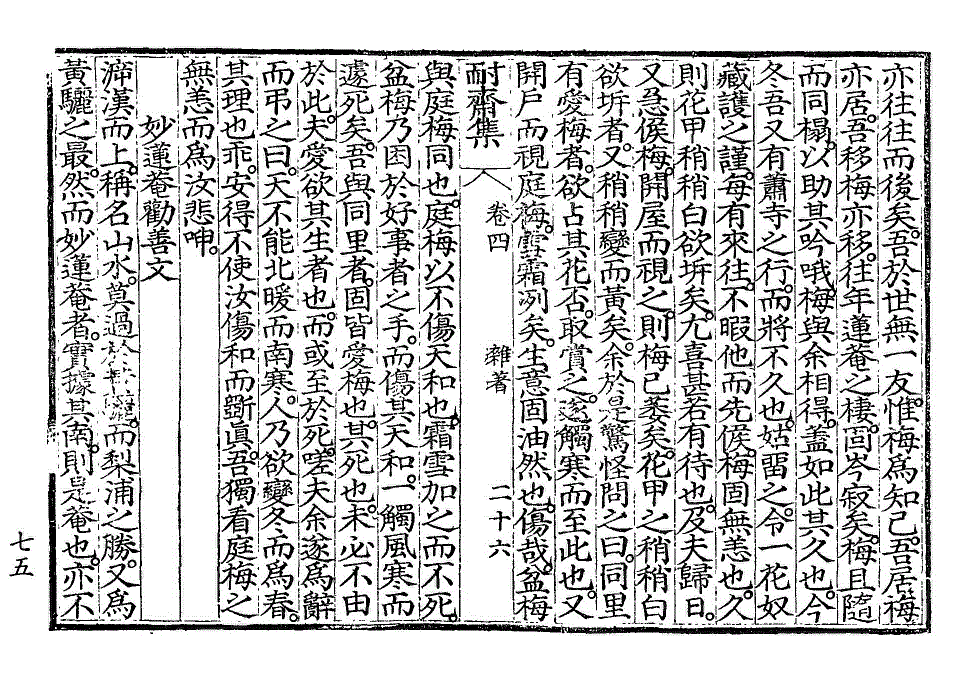 亦往往而后矣。吾于世无一友。惟梅为知己。吾居梅亦居。吾移梅亦移。往年莲庵之栖。固岑寂矣。梅且随而同榻。以助其吟哦。梅与余相得。盖如此其久也。今冬吾又有萧寺之行。而将不久也。姑留之。令一花奴藏护之谨。每有来往。不暇他而先候。梅固无恙也。久则花甲稍稍白欲坼矣。尤喜甚若有待也。及夫归日。又急候梅。开屋而视之。则梅已萎矣。花甲之稍稍白欲坼者。又稍稍变而黄矣。余于是惊怪问之曰。同里有爱梅者。欲占其花否。取赏之。遂触寒而至此也。又开户而视庭梅。雪霜冽矣。生意固油然也。伤哉。盆梅与庭梅同也。庭梅以不伤天和也。霜雪加之而不死。盆梅乃困于好事者之手。而伤其天和。一触风寒而遽死矣。吾与同里者。固皆爱梅也。其死也。未必不由于此。夫爱欲其生者也。而或至于死。嗟夫余遂为辞而吊之曰。天不能北暖而南寒。人乃欲变冬而为春。其理也乖。安得不使汝伤和而斲真。吾独看庭梅之无恙而为汝悲呻。
亦往往而后矣。吾于世无一友。惟梅为知己。吾居梅亦居。吾移梅亦移。往年莲庵之栖。固岑寂矣。梅且随而同榻。以助其吟哦。梅与余相得。盖如此其久也。今冬吾又有萧寺之行。而将不久也。姑留之。令一花奴藏护之谨。每有来往。不暇他而先候。梅固无恙也。久则花甲稍稍白欲坼矣。尤喜甚若有待也。及夫归日。又急候梅。开屋而视之。则梅已萎矣。花甲之稍稍白欲坼者。又稍稍变而黄矣。余于是惊怪问之曰。同里有爱梅者。欲占其花否。取赏之。遂触寒而至此也。又开户而视庭梅。雪霜冽矣。生意固油然也。伤哉。盆梅与庭梅同也。庭梅以不伤天和也。霜雪加之而不死。盆梅乃困于好事者之手。而伤其天和。一触风寒而遽死矣。吾与同里者。固皆爱梅也。其死也。未必不由于此。夫爱欲其生者也。而或至于死。嗟夫余遂为辞而吊之曰。天不能北暖而南寒。人乃欲变冬而为春。其理也乖。安得不使汝伤和而斲真。吾独看庭梅之无恙而为汝悲呻。妙莲庵劝善文
溯汉而上。称名山水。莫过于黄骊。而梨浦之胜。又为黄骊之最。然而妙莲庵者。实据其南。则是庵也。亦不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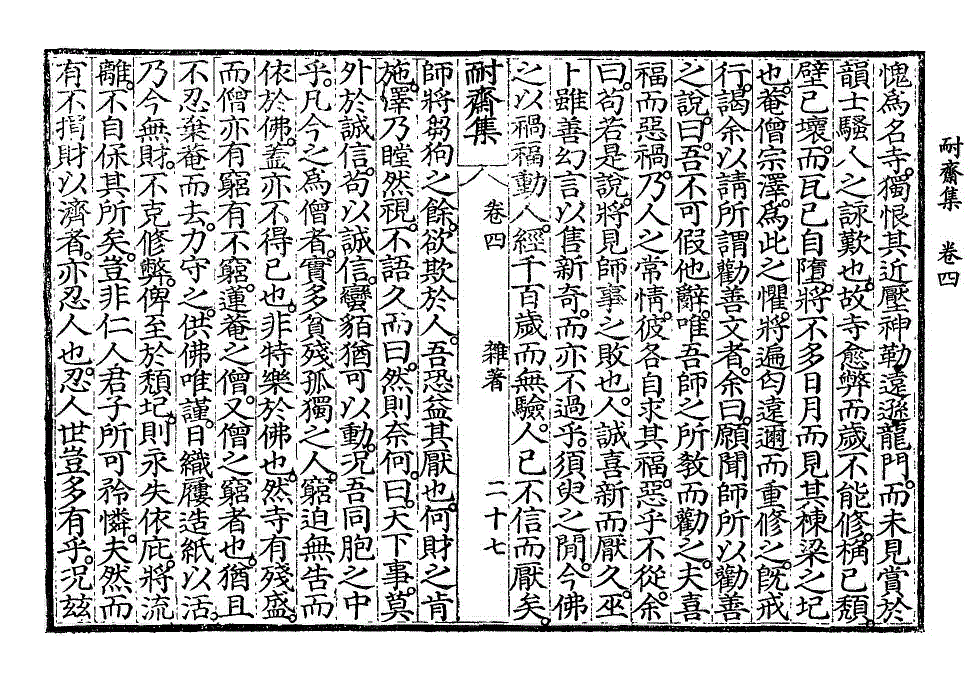 愧为名寺。独恨其近压神勒,远逊,龙门。而未见赏于韵士骚人之咏叹也。故寺愈弊而岁不能修。桷已颓。壁已坏。而瓦已自堕。将不多日月而见其栋梁之圮也。庵僧宗泽。为此之惧。将遍丐远迩而重修之。既戒行。谒余以请所谓劝善文者。余曰。愿闻师所以劝善之说。曰。吾不可假他辞。唯吾师之所教而劝之。夫喜福而恶祸。乃人之常情。彼各自求其福。恶乎不从。余曰。苟若是说。将见师事之败也。人诚喜新而厌久。巫卜虽善幻言以售新奇。而亦不过乎。须臾之间。今佛之以祸福动人。经千百岁而无验。人已不信而厌矣。师将刍狗之馀。欲欺于人。吾恐益其厌也。何财之肯施。泽乃瞠然视。不语久而曰。然则奈何。曰。天下事。莫外于诚信。苟以诚信。蛮貊犹可以动。况吾同胞之中乎。凡今之为僧者。实多贫残孤独之人。穷迫无告而依于佛。盖亦不得已也。非特乐于佛也。然寺有残盛。而僧亦有穷有不穷。莲庵之僧。又僧之穷者也。犹且不忍弃庵而去。力守之。供佛唯谨。日织屦造纸以活。乃今无财。不克修弊。俾至于颓圮。则永失依庇。将流离。不自保其所矣。岂非仁人君子所可矜怜。夫然而有不捐财以济者。亦忍人也。忍人世岂多有乎。况玆
愧为名寺。独恨其近压神勒,远逊,龙门。而未见赏于韵士骚人之咏叹也。故寺愈弊而岁不能修。桷已颓。壁已坏。而瓦已自堕。将不多日月而见其栋梁之圮也。庵僧宗泽。为此之惧。将遍丐远迩而重修之。既戒行。谒余以请所谓劝善文者。余曰。愿闻师所以劝善之说。曰。吾不可假他辞。唯吾师之所教而劝之。夫喜福而恶祸。乃人之常情。彼各自求其福。恶乎不从。余曰。苟若是说。将见师事之败也。人诚喜新而厌久。巫卜虽善幻言以售新奇。而亦不过乎。须臾之间。今佛之以祸福动人。经千百岁而无验。人已不信而厌矣。师将刍狗之馀。欲欺于人。吾恐益其厌也。何财之肯施。泽乃瞠然视。不语久而曰。然则奈何。曰。天下事。莫外于诚信。苟以诚信。蛮貊犹可以动。况吾同胞之中乎。凡今之为僧者。实多贫残孤独之人。穷迫无告而依于佛。盖亦不得已也。非特乐于佛也。然寺有残盛。而僧亦有穷有不穷。莲庵之僧。又僧之穷者也。犹且不忍弃庵而去。力守之。供佛唯谨。日织屦造纸以活。乃今无财。不克修弊。俾至于颓圮。则永失依庇。将流离。不自保其所矣。岂非仁人君子所可矜怜。夫然而有不捐财以济者。亦忍人也。忍人世岂多有乎。况玆耐斋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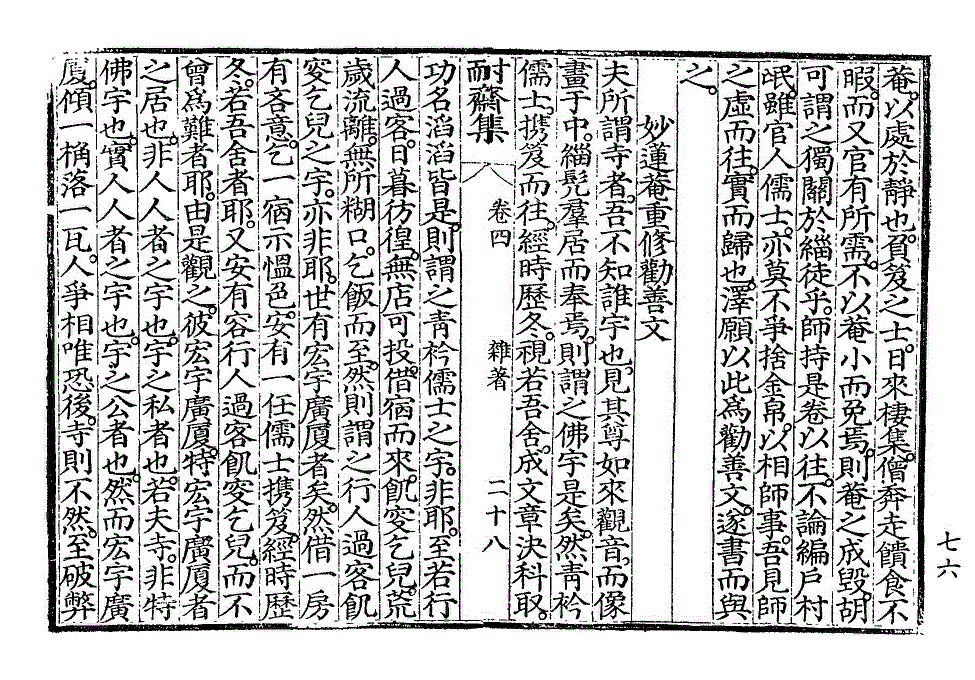 庵。以处于静也。负笈之士。日来栖集。僧奔走馈食不暇。而又官有所需。不以庵小而免焉。则庵之成毁。胡可谓之独关于缁徒乎。师持是卷以往。不论编户村氓。虽官人儒士。亦莫不争舍金帛。以相师事。吾见师之虚而往。实而归也。泽愿以此为劝善文。遂书而与之。
庵。以处于静也。负笈之士。日来栖集。僧奔走馈食不暇。而又官有所需。不以庵小而免焉。则庵之成毁。胡可谓之独关于缁徒乎。师持是卷以往。不论编户村氓。虽官人儒士。亦莫不争舍金帛。以相师事。吾见师之虚而往。实而归也。泽愿以此为劝善文。遂书而与之。妙莲庵重修劝善文
夫所谓寺者。吾不知谁宇也。见其尊如来观音。而像画于中。缁髡群居而奉焉。则谓之佛宇是矣。然青衿儒士。携笈而往。经时历冬。视若吾舍。成文章决科取。功名滔滔皆是。则谓之青衿儒士之宇。非耶。至若行人过客。日暮彷徨。无店可投。借宿而来。饥叟乞儿。荒岁流离。无所糊口。乞饭而至。然则谓之行人过客饥叟乞儿之宇。亦非耶。世有宏宇广厦者矣。然借一房有吝意。乞一宿示愠色。安有一任儒士携笈。经时历冬。若吾舍者耶。又安有容行人过客饥叟乞儿。而不曾为难者耶。由是观之。彼宏宇广厦。特宏宇广厦者之居也。非人人者之宇也。宇之私者也。若夫寺。非特佛宇也。实人人者之宇也。宇之公者也。然而宏宇广厦。倾一桷落一瓦。人争相唯恐后。寺则不然。至破弊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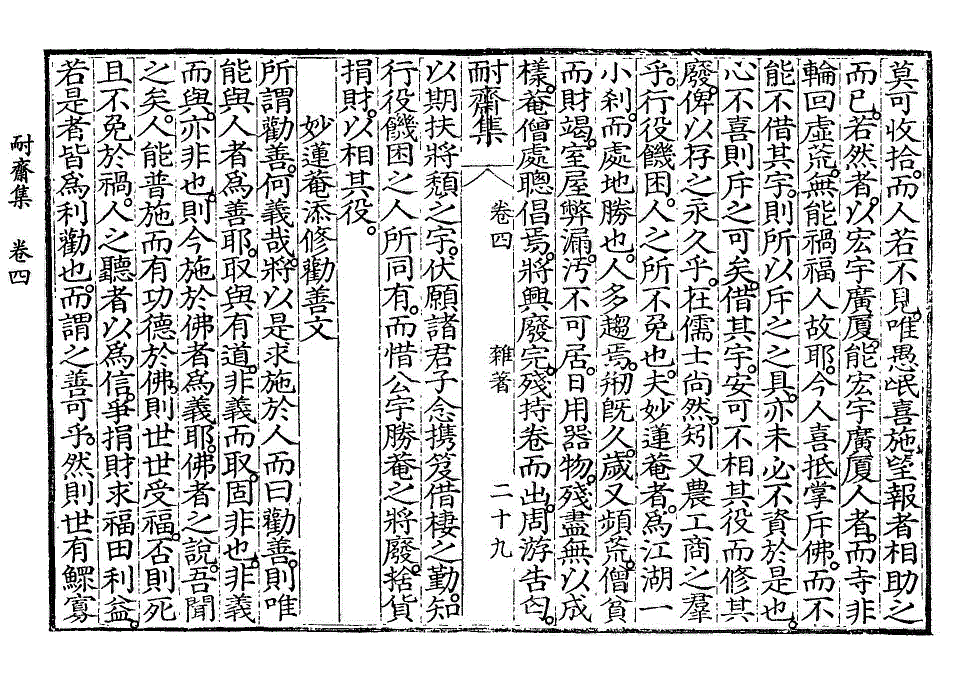 莫可收拾。而人若不见。唯愚氓喜施望报者相助之而已。若然者。以宏宇广厦。能宏宇广厦人者。而寺非轮回虚荒。无能祸福人故耶。今人喜抵掌斥佛。而不能不借其宇。则所以斥之之具。亦未必不资于是也。心不喜则斥之可矣。借其宇。安可不相其役而修其废。俾以存之永久乎。在儒士尚然。矧又农工商之群乎。行役饥困。人之所不免也。夫妙莲庵者。为江湖一小刹。而处地胜也。人多趋焉。刱既久。岁又频荒。僧贫而财竭。室屋弊漏。污不可居。日用器物。残尽无以成样。庵僧处聪倡焉。将兴废完。残持卷而出。周游告丐。以期扶将颓之宇。伏愿诸君子念携笈借栖之勤。知行役饥困之人所同有。而惜公宇胜庵之将废。舍货捐财。以相其役。
莫可收拾。而人若不见。唯愚氓喜施望报者相助之而已。若然者。以宏宇广厦。能宏宇广厦人者。而寺非轮回虚荒。无能祸福人故耶。今人喜抵掌斥佛。而不能不借其宇。则所以斥之之具。亦未必不资于是也。心不喜则斥之可矣。借其宇。安可不相其役而修其废。俾以存之永久乎。在儒士尚然。矧又农工商之群乎。行役饥困。人之所不免也。夫妙莲庵者。为江湖一小刹。而处地胜也。人多趋焉。刱既久。岁又频荒。僧贫而财竭。室屋弊漏。污不可居。日用器物。残尽无以成样。庵僧处聪倡焉。将兴废完。残持卷而出。周游告丐。以期扶将颓之宇。伏愿诸君子念携笈借栖之勤。知行役饥困之人所同有。而惜公宇胜庵之将废。舍货捐财。以相其役。妙莲庵添修劝善文
所谓劝善。何义哉。将以是求施于人而曰劝善。则唯能与人者为善耶。取与有道。非义而取。固非也。非义而与。亦非也。则今施于佛者为义耶。佛者之说。吾闻之矣。人能普施而有功德于佛。则世世受福。否则死且不免于祸。人之听者以为信。争捐财求福田利益。若是者皆为利劝也。而谓之善可乎。然则世有鳏寡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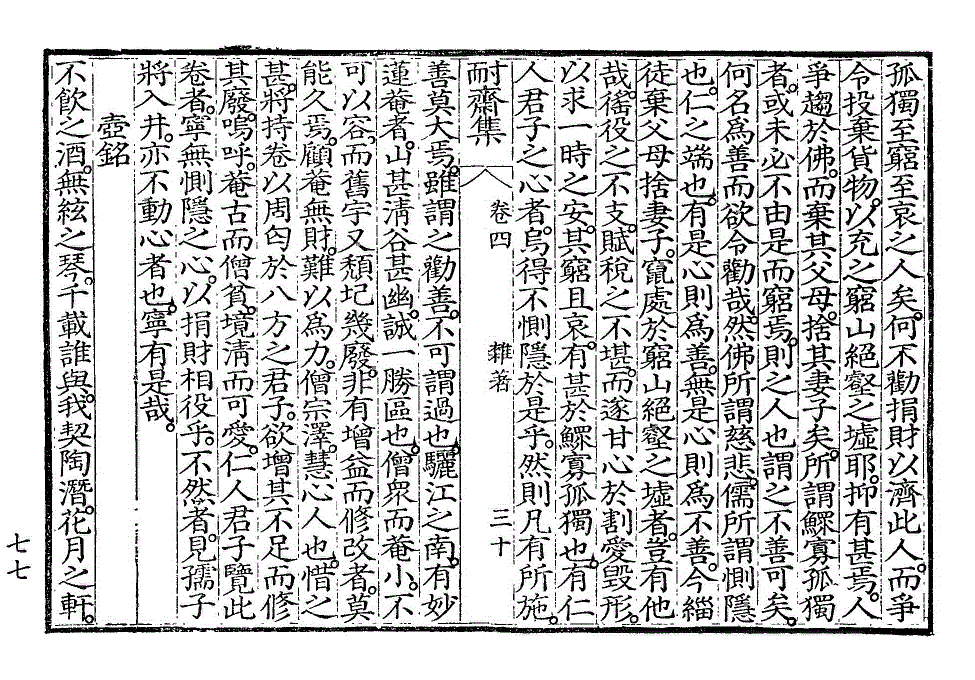 孤独至穷至哀之人矣。何不劝捐财以济此人。而争令投弃货物。以充之穷山绝壑之墟耶。抑有甚焉。人争趋于佛。而弃其父母。舍其妻子矣。所谓鳏寡孤独者。或未必不由是而穷焉。则之人也谓之不善可矣。何名为善而欲令劝哉。然佛所谓慈悲。儒所谓恻隐也。仁之端也。有是心则为善。无是心则为不善。今缁徒弃父母舍妻子。窜处于穷山绝壑之墟者。岂有他哉。徭役之不支。赋税之不堪。而遂甘心于割爱毁形。以求一时之安。其穷且哀。有甚于鳏寡孤独也。有仁人君子之心者。乌得不恻隐于是乎。然则凡有所施。善莫大焉。虽谓之劝善。不可谓过也。骊江之南。有妙莲庵者。山甚清谷甚幽。诚一胜区也。僧众而庵小。不可以容。而旧宇又颓圮几废。非有增益而修改者。莫能久焉。顾庵无财。难以为力。僧宗泽。慧心人也。惜之甚。将持卷以周丐于八方之君子。欲增其不足而修其废。呜呼。庵古而僧贫。境清而可爱。仁人君子览此卷者。宁无恻隐之心。以捐财相役乎。不然者。见孺子将入井。亦不动心者也。宁有是哉。
孤独至穷至哀之人矣。何不劝捐财以济此人。而争令投弃货物。以充之穷山绝壑之墟耶。抑有甚焉。人争趋于佛。而弃其父母。舍其妻子矣。所谓鳏寡孤独者。或未必不由是而穷焉。则之人也谓之不善可矣。何名为善而欲令劝哉。然佛所谓慈悲。儒所谓恻隐也。仁之端也。有是心则为善。无是心则为不善。今缁徒弃父母舍妻子。窜处于穷山绝壑之墟者。岂有他哉。徭役之不支。赋税之不堪。而遂甘心于割爱毁形。以求一时之安。其穷且哀。有甚于鳏寡孤独也。有仁人君子之心者。乌得不恻隐于是乎。然则凡有所施。善莫大焉。虽谓之劝善。不可谓过也。骊江之南。有妙莲庵者。山甚清谷甚幽。诚一胜区也。僧众而庵小。不可以容。而旧宇又颓圮几废。非有增益而修改者。莫能久焉。顾庵无财。难以为力。僧宗泽。慧心人也。惜之甚。将持卷以周丐于八方之君子。欲增其不足而修其废。呜呼。庵古而僧贫。境清而可爱。仁人君子览此卷者。宁无恻隐之心。以捐财相役乎。不然者。见孺子将入井。亦不动心者也。宁有是哉。壶铭
不饮之酒。无弦之琴。千载谁与。我契陶潜。花月之轩。
耐斋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聊以啸吟。适意即止。奚弹奚斟。
聊以啸吟。适意即止。奚弹奚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