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x 页
西堂私载卷之三
书
书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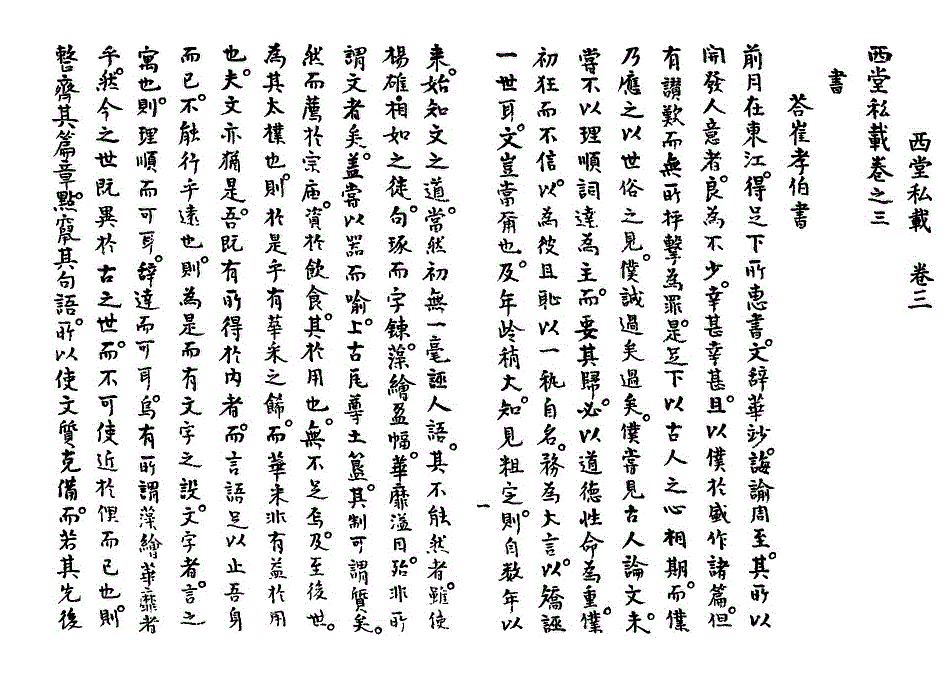 答崔孝伯书
答崔孝伯书前月在东江。得足下所惠书。文辞华妙。诲谕周至。其所以开发人意者。良为不少。幸甚幸甚。且以仆于盛作诸篇。但有赞叹而无所抨击为罪。是足下以古人之心相期。而仆乃应之以世俗之见。仆诚过矣过矣。仆尝见古人论文。未尝不以理顺词达为主。而要其归。必以道德性命为重。仆初狂而不信。以为彼且耻以一秇自名。务为大言。以矫诬一世耳。文岂当尔也。及年龄稍大。知见粗定。则自数年以来。始知文之道。当然初无一毫诬人语。其不能然者。虽使扬雄,相如之徒。句琢而字鍊。藻绘盈幅。华靡溢目。殆非所谓文者矣。盖尝以器而喻。上古瓦尊土簋。其制可谓质矣。然而荐于宗庙。资于饮食。其于用也。无不足焉。及至后世。为其太朴也。则于是乎有华采之饰。而华采非有益于用也。夫文亦犹是。吾既有所得于内者。而言语足以止吾身而已。不能行乎远也。则为是而有文字之设。文字者。言之寓也。则理顺而可耳。辞达而可耳。乌有所谓藻绘华靡者乎。然今之世既异于古之世。而不可使近于俚而已也。则整齐其篇章。点窜其句语。所以使文质克备。而若其先后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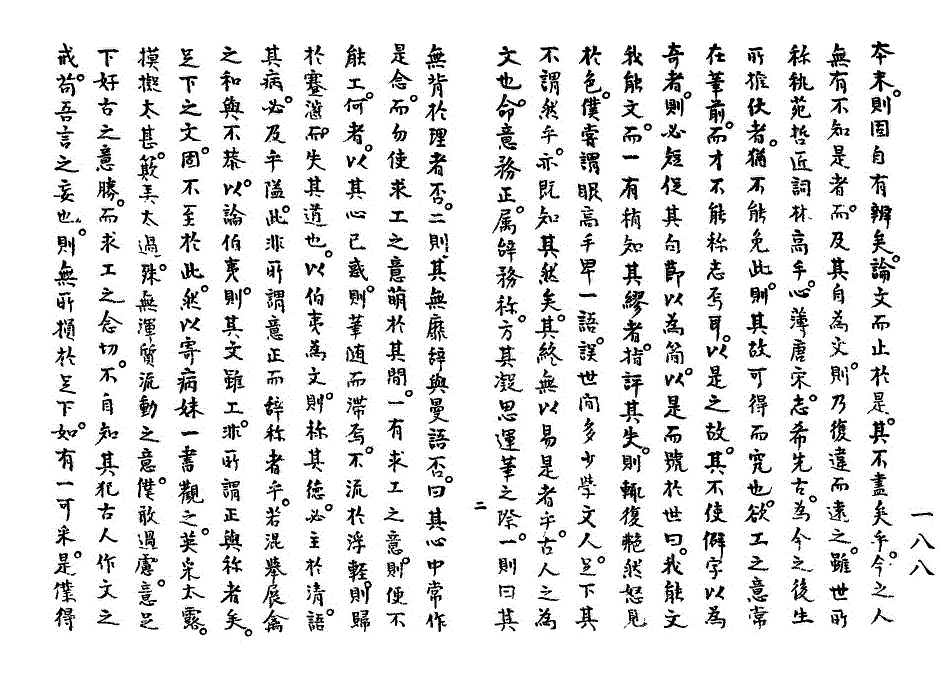 本末。则固自有辨矣。论文而止于是。其不尽矣乎。今之人无有不知是者。而及其自为文。则乃复违而远之。虽世所称秇苑哲匠词林高手。心薄唐宋。志希先古。为今之后生所推伏者。犹不能免此。则其故可得而究也。欲工之意常在笔前。而才不能称志焉耳。以是之故。其不使僻字以为奇者。则必短促其句节以为简。以是而号于世曰。我能文我能文。而一有稍知其缪者。指评其失。则辄复艴然怒见于色。仆尝谓眼高手卑一语。误世间多少学文人。足下其不谓然乎。亦既知其然矣。其终无以易是者乎。古人之为文也。命意务正。属辞务称。方其凝思运笔之际。一则曰其无背于理者否。二则其无靡辞与曼语否。曰其心中常作是念。而勿使求工之意萌于其间。一有求工之意。则便不能工。何者。以其心已惑。则笔随而滞焉。不流于浮轻。则归于蹇𤁧。而失其道也。以伯夷为文。则称其德。必主于清。语其病。必及乎隘。此非所谓意正而辞称者乎。若混举展禽之和与不恭。以论伯夷。则其文虽工。非所谓正与称者矣。足下之文。固不至于此。然以寄病妹一书观之。英采太露。摸拟太甚。簸弄太过。殊无浑质流动之意。仆敢过虑。意足下好古之意胜。而求工之念切。不自知其犯古人作文之戒。苟吾言之妄也。则无所损于足下。如有一可采。是仆得
本末。则固自有辨矣。论文而止于是。其不尽矣乎。今之人无有不知是者。而及其自为文。则乃复违而远之。虽世所称秇苑哲匠词林高手。心薄唐宋。志希先古。为今之后生所推伏者。犹不能免此。则其故可得而究也。欲工之意常在笔前。而才不能称志焉耳。以是之故。其不使僻字以为奇者。则必短促其句节以为简。以是而号于世曰。我能文我能文。而一有稍知其缪者。指评其失。则辄复艴然怒见于色。仆尝谓眼高手卑一语。误世间多少学文人。足下其不谓然乎。亦既知其然矣。其终无以易是者乎。古人之为文也。命意务正。属辞务称。方其凝思运笔之际。一则曰其无背于理者否。二则其无靡辞与曼语否。曰其心中常作是念。而勿使求工之意萌于其间。一有求工之意。则便不能工。何者。以其心已惑。则笔随而滞焉。不流于浮轻。则归于蹇𤁧。而失其道也。以伯夷为文。则称其德。必主于清。语其病。必及乎隘。此非所谓意正而辞称者乎。若混举展禽之和与不恭。以论伯夷。则其文虽工。非所谓正与称者矣。足下之文。固不至于此。然以寄病妹一书观之。英采太露。摸拟太甚。簸弄太过。殊无浑质流动之意。仆敢过虑。意足下好古之意胜。而求工之念切。不自知其犯古人作文之戒。苟吾言之妄也。则无所损于足下。如有一可采。是仆得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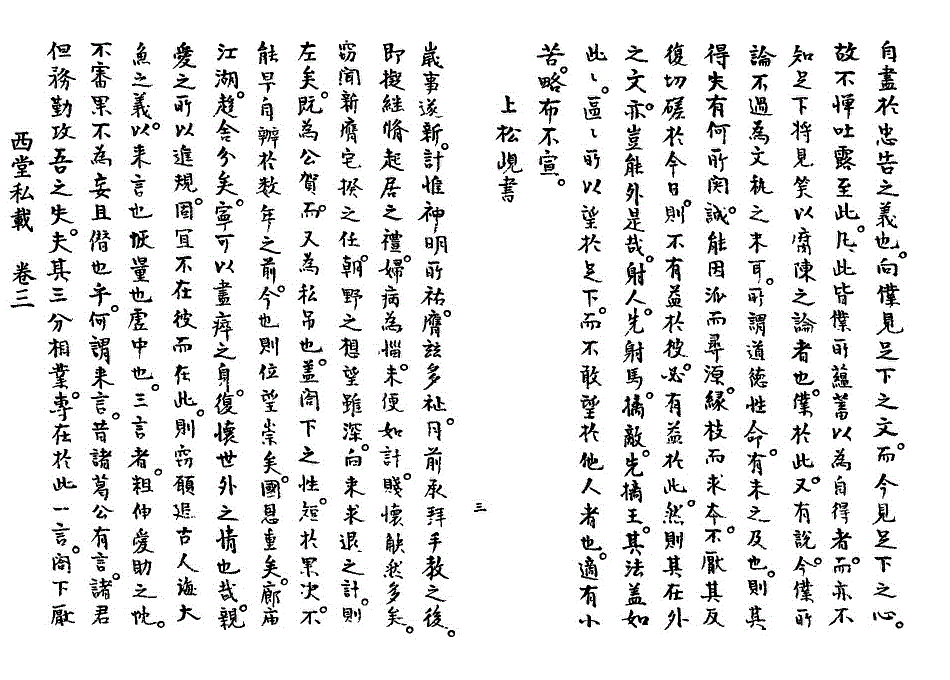 自尽于忠告之义也。向仆见足下之文。而今见足下之心。故不惮吐露至此。凡此皆仆所蕴蓄以为自得者。而亦不知足下将见笑以腐陈之论者也。仆于此。又有说。今仆所论不过为文秇之末耳。所谓道德性命。有未之及也。则其得失有何所关。诚能因派而寻源。缘枝而求本。不厌其反复切磋于今日。则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然则其在外之文。亦岂能外是哉。射人。先射马。擒敌。先擒王。其法盖如此此。区区所以望于足下。而不敢望于他人者也。适有小苦。略布不宣。
自尽于忠告之义也。向仆见足下之文。而今见足下之心。故不惮吐露至此。凡此皆仆所蕴蓄以为自得者。而亦不知足下将见笑以腐陈之论者也。仆于此。又有说。今仆所论不过为文秇之末耳。所谓道德性命。有未之及也。则其得失有何所关。诚能因派而寻源。缘枝而求本。不厌其反复切磋于今日。则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然则其在外之文。亦岂能外是哉。射人。先射马。擒敌。先擒王。其法盖如此此。区区所以望于足下。而不敢望于他人者也。适有小苦。略布不宣。上松岘书
岁事遂新。计惟神明所祐。膺玆多祉。月前承拜手教之后。即拟继脩起居之礼。妇病为恼。未便如计。贱怀觖然多矣。窃闻新膺宅揆之任。朝野之想望虽深。向来求退之计。则左矣。既为公贺。而又为私吊也。盖閤下之性。短于果决。不能早自办于数年之前。今也则位望崇矣。国恩重矣。廊庙江湖。趍舍分矣。宁可以尽瘁之身。复怀世外之情也哉。亲爱之所以进规。固宜不在彼而在此。则窃愿追古人海大鱼之义。以来言也恢量也虚中也。三言者。粗伸爱助之忱。不审果不为妄且僭也乎。何谓来言。昔诸葛公有言。诸君但务勤攻吾之失。夫其三分相业。专在于此一言。閤下厌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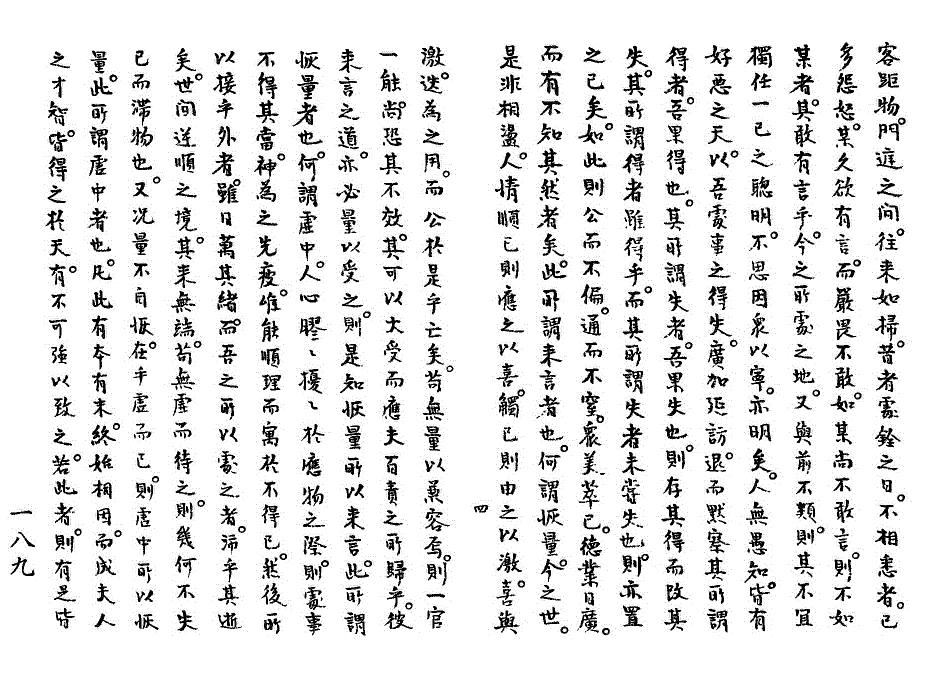 客距物。门庭之间。往来如扫。昔者处铨之日。不相悉者。已多怨怒。某久欲有言。而严畏不敢。如某尚不敢言。则不如某者。其敢有言乎。今之所处之地。又与前不类。则其不宜独任一己之聪明。不思因众以宁。亦明矣。人无愚知。皆有好恶之天。以吾处事之得失。广加延访。退而默察其所谓得者。吾果得也。其所谓失者。吾果失也。则存其得而改其失。其所谓得者虽得乎。而其所谓失者未尝失也。则亦置之已矣。如此则公而不偏。通而不窒。众美萃己。德业日广。而有不知其然者矣。此所谓来言者也。何谓恢量。今之世。是非相荡。人情顺己则应之以喜。触己则由之以激。喜与激。迭为之用。而公于是乎亡矣。苟无量以兼容焉。则一官一能。尚恐其不效。其可以大受而应夫百责之所归乎。彼来言之道。亦必量以受之。则是知恢量所以来言。此所谓恢量者也。何谓虚中。人心胶胶扰扰于应物之际。则处事不得其当。神为之先疲。唯能顺理而寓于不得已。然后所以接乎外者。虽日万其绪。而吾之所以处之者。沛乎其逝矣。世间逆顺之境。其来无端。苟无虚而待之。则几何不失己而滞物也。又况量不自恢。在乎虚而已。则虚中所以恢量。此所谓虚中者也。凡此有本有末。终始相因。而成夫人之才智。皆得之于天。有不可强以致之。若此者。则有足皆
客距物。门庭之间。往来如扫。昔者处铨之日。不相悉者。已多怨怒。某久欲有言。而严畏不敢。如某尚不敢言。则不如某者。其敢有言乎。今之所处之地。又与前不类。则其不宜独任一己之聪明。不思因众以宁。亦明矣。人无愚知。皆有好恶之天。以吾处事之得失。广加延访。退而默察其所谓得者。吾果得也。其所谓失者。吾果失也。则存其得而改其失。其所谓得者虽得乎。而其所谓失者未尝失也。则亦置之已矣。如此则公而不偏。通而不窒。众美萃己。德业日广。而有不知其然者矣。此所谓来言者也。何谓恢量。今之世。是非相荡。人情顺己则应之以喜。触己则由之以激。喜与激。迭为之用。而公于是乎亡矣。苟无量以兼容焉。则一官一能。尚恐其不效。其可以大受而应夫百责之所归乎。彼来言之道。亦必量以受之。则是知恢量所以来言。此所谓恢量者也。何谓虚中。人心胶胶扰扰于应物之际。则处事不得其当。神为之先疲。唯能顺理而寓于不得已。然后所以接乎外者。虽日万其绪。而吾之所以处之者。沛乎其逝矣。世间逆顺之境。其来无端。苟无虚而待之。则几何不失己而滞物也。又况量不自恢。在乎虚而已。则虚中所以恢量。此所谓虚中者也。凡此有本有末。终始相因。而成夫人之才智。皆得之于天。有不可强以致之。若此者。则有足皆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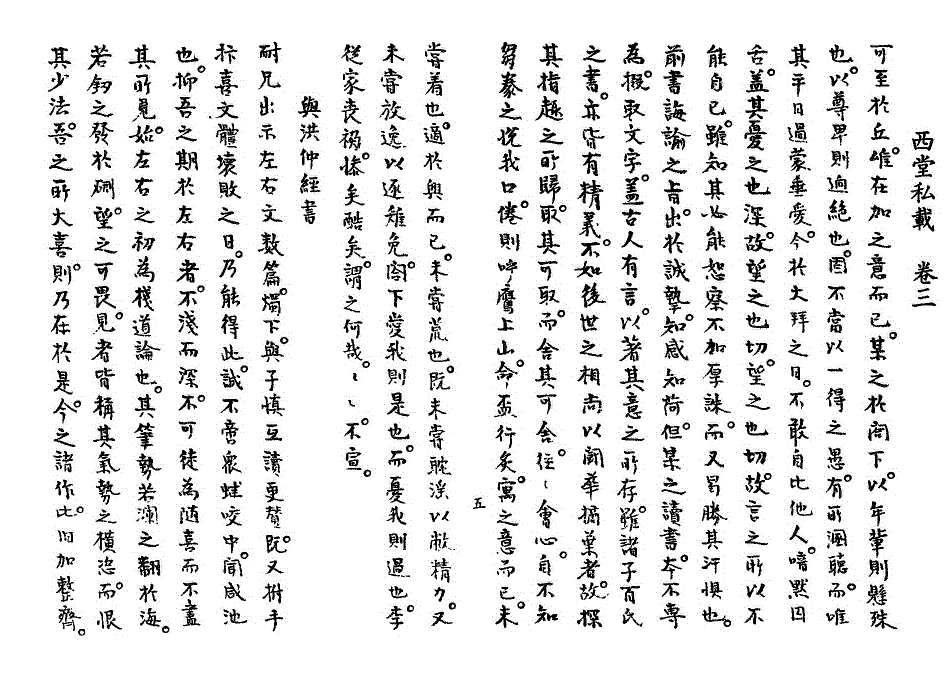 可至于丘。唯在加之意而已。某之于閤下。以年辈则悬殊也。以尊卑则迥绝也。固不当以一得之愚。有所溷听。而唯其平日过蒙垂爱。今于大拜之日。不敢自比他人。喑默囚舌。盖其忧之也深。故望之也切。望之也切。故言之所以不能自已。虽知其必能恕察不加厚诛。而又曷胜其汗惧也。前书诲谕之旨。出于诚挚。知感知荷。但某之读书。本不专为。掇取文字。盖古人有言。以著其意之所存。虽诸子百氏之书。亦皆有精义。不如后世之相尚以斗华摘叶者。故探其指趣之所归。取其可取。而舍其可舍。往往会心。自不知刍豢之悦我口。倦则呼鹰上山。命杯行炙。寓之意而已。未尝着也。适于兴而已。未尝荒也。既未尝耽淫以敝精力。又未尝放逸以逐雉兔。閤下爱我则是也。而忧我则过也。李从家丧祸。惨矣酷矣。谓之何哉。何哉。不宣。
可至于丘。唯在加之意而已。某之于閤下。以年辈则悬殊也。以尊卑则迥绝也。固不当以一得之愚。有所溷听。而唯其平日过蒙垂爱。今于大拜之日。不敢自比他人。喑默囚舌。盖其忧之也深。故望之也切。望之也切。故言之所以不能自已。虽知其必能恕察不加厚诛。而又曷胜其汗惧也。前书诲谕之旨。出于诚挚。知感知荷。但某之读书。本不专为。掇取文字。盖古人有言。以著其意之所存。虽诸子百氏之书。亦皆有精义。不如后世之相尚以斗华摘叶者。故探其指趣之所归。取其可取。而舍其可舍。往往会心。自不知刍豢之悦我口。倦则呼鹰上山。命杯行炙。寓之意而已。未尝着也。适于兴而已。未尝荒也。既未尝耽淫以敝精力。又未尝放逸以逐雉兔。閤下爱我则是也。而忧我则过也。李从家丧祸。惨矣酷矣。谓之何哉。何哉。不宣。与洪仲经书
耐兄出示左右文数篇。烛下。与子慎互读更赞。既又拊手抃喜文体坏败之日。乃能得此。诚不啻众蛙咬中。闻咸池也。抑吾之期于左右者。不浅而深。不可徒为随喜而不尽其所见。始左右之初为栈道论也。其笔势若澜之翻于海。若釰之发于硎。望之可畏。见者皆称其气势之横恣。而恨其少法。吾之所大喜。则乃在于是。今之诸作。比旧加整齐。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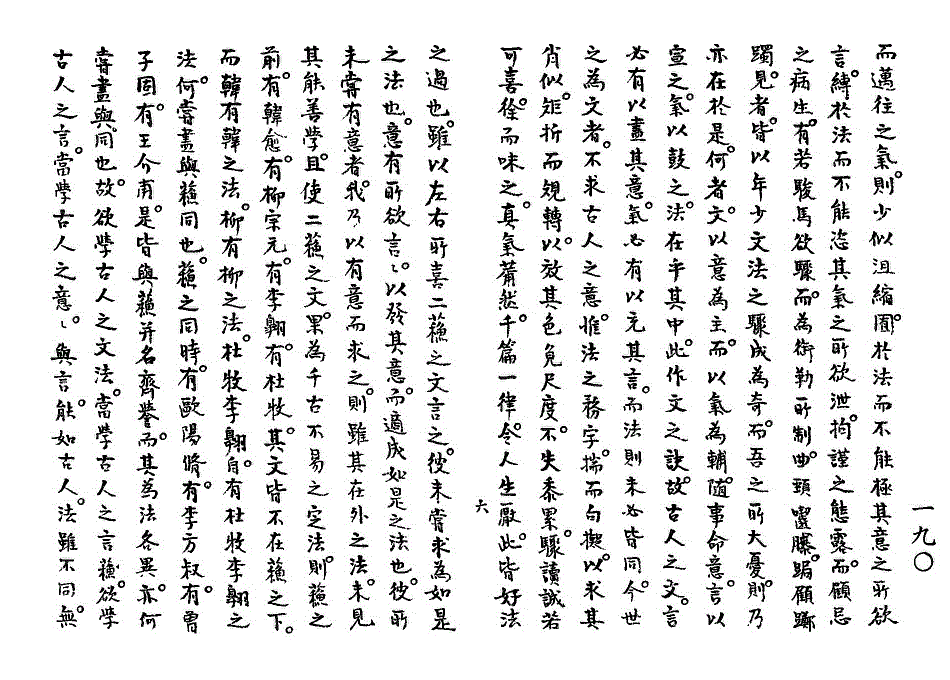 而迈往之气。则少似沮缩。囿于法而不能极其意之所欲言。缚于法而不能恣其气之所欲泄。拘谨之态露。而顾忌之病生。有若骏马欲骤。而为衔勒所制。曲颈齧膝。跼顾踯躅。见者。皆以年少文法之骤成为奇。而吾之所大忧。则乃亦在于是。何者。文以意为主。而以气为辅。随事命意。言以宣之。气以鼓之。法在乎其中。此作文之诀。故古人之文。言必有以尽其意。气必有以充其言。而法则未必皆同。今世之为文者。不求古人之意。惟法之务字。揣而句拟。以求其肖似。矩折而规转。以效其色皃尺度。不失黍累。骤读诚若可喜。徐而味之。真气薾然。千篇一律。令人生厌。此皆好法之过也。虽以左右所喜二苏之文言之。彼未尝求为如是之法也。意有所欲言。言以发其意。而适成如是之法也。彼所未尝有意者。我乃以有意而求之。则虽其在外之法。未见其能善学。且使二苏之文。果为千古不易之定法。则苏之前。有韩愈。有柳宗元。有李翱。有杜牧。其文皆不在苏之下。而韩有韩之法。柳有柳之法。杜牧李翱。自有杜牧李翱之法。何尝尽与苏同也。苏之同时。有欧阳脩。有李方叔。有曾子固。有王介甫。是皆与苏并名齐誉。而其为法各异。亦何尝尽与苏同也。故欲学古人之文法。当学古人之言。欲学古人之言。当学古人之意。意与言。能如古人。法虽不同。无
而迈往之气。则少似沮缩。囿于法而不能极其意之所欲言。缚于法而不能恣其气之所欲泄。拘谨之态露。而顾忌之病生。有若骏马欲骤。而为衔勒所制。曲颈齧膝。跼顾踯躅。见者。皆以年少文法之骤成为奇。而吾之所大忧。则乃亦在于是。何者。文以意为主。而以气为辅。随事命意。言以宣之。气以鼓之。法在乎其中。此作文之诀。故古人之文。言必有以尽其意。气必有以充其言。而法则未必皆同。今世之为文者。不求古人之意。惟法之务字。揣而句拟。以求其肖似。矩折而规转。以效其色皃尺度。不失黍累。骤读诚若可喜。徐而味之。真气薾然。千篇一律。令人生厌。此皆好法之过也。虽以左右所喜二苏之文言之。彼未尝求为如是之法也。意有所欲言。言以发其意。而适成如是之法也。彼所未尝有意者。我乃以有意而求之。则虽其在外之法。未见其能善学。且使二苏之文。果为千古不易之定法。则苏之前。有韩愈。有柳宗元。有李翱。有杜牧。其文皆不在苏之下。而韩有韩之法。柳有柳之法。杜牧李翱。自有杜牧李翱之法。何尝尽与苏同也。苏之同时。有欧阳脩。有李方叔。有曾子固。有王介甫。是皆与苏并名齐誉。而其为法各异。亦何尝尽与苏同也。故欲学古人之文法。当学古人之言。欲学古人之言。当学古人之意。意与言。能如古人。法虽不同。无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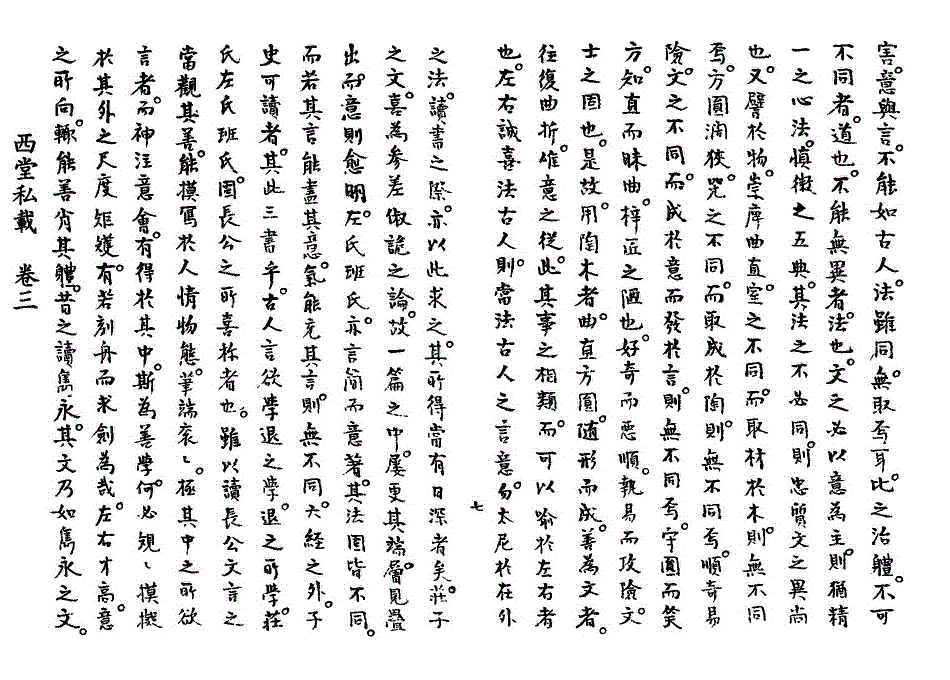 害。意与言。不能如古人。法虽同。无取焉耳。比之治体。不可不同者。道也。不能无异者。法也。文之必以意为主。则犹精一之心法。慎徽之五典。其法之不必同。则忠质文之异尚也。又譬于物。崇庳曲直。室之不同。而取材于木。则无不同焉。方圆阔狭。器之不同。而取成于陶。则无不同焉。顺奇易险。文之不同。而成于意而发于言。则无不同焉。守圆而笑方。知直而昧曲。梓匠之陋也。好奇而恶顺。执易而攻险。文士之固也。是故。用陶木者。曲直方圆。随形而成。善为文者。往复曲折。唯意之从。此其事之相类。而可以喻于左右者也。左右诚喜法古人。则当法古人之言意。勿太尼于在外之法。读书之际。亦以此求之。其所得当有日深者矣。庄子之文。喜为参差俶诡之论。故一篇之中。屡更其端。层见叠出。而意则愈明。左氏班氏。亦言简而意著。其法固皆不同。而若其言能尽其意。气能充其言。则无不同。六经之外。子史可读者。其此三书乎。古人言欲学退之学。退之所学。庄氏左氏班氏。固长公之所喜称者也。虽以读长公文言之当观其善。能摸写于人情物态。笔端衮衮。极其中之所欲言者。而神注意会。有得于其中。斯为善学。何必规规摸拟于其外之尺度矩矱。有若刻舟而求剑为哉。左右才高。意之所向。辄能善肖其体。昔之读隽永。其文乃如隽永之文。
害。意与言。不能如古人。法虽同。无取焉耳。比之治体。不可不同者。道也。不能无异者。法也。文之必以意为主。则犹精一之心法。慎徽之五典。其法之不必同。则忠质文之异尚也。又譬于物。崇庳曲直。室之不同。而取材于木。则无不同焉。方圆阔狭。器之不同。而取成于陶。则无不同焉。顺奇易险。文之不同。而成于意而发于言。则无不同焉。守圆而笑方。知直而昧曲。梓匠之陋也。好奇而恶顺。执易而攻险。文士之固也。是故。用陶木者。曲直方圆。随形而成。善为文者。往复曲折。唯意之从。此其事之相类。而可以喻于左右者也。左右诚喜法古人。则当法古人之言意。勿太尼于在外之法。读书之际。亦以此求之。其所得当有日深者矣。庄子之文。喜为参差俶诡之论。故一篇之中。屡更其端。层见叠出。而意则愈明。左氏班氏。亦言简而意著。其法固皆不同。而若其言能尽其意。气能充其言。则无不同。六经之外。子史可读者。其此三书乎。古人言欲学退之学。退之所学。庄氏左氏班氏。固长公之所喜称者也。虽以读长公文言之当观其善。能摸写于人情物态。笔端衮衮。极其中之所欲言者。而神注意会。有得于其中。斯为善学。何必规规摸拟于其外之尺度矩矱。有若刻舟而求剑为哉。左右才高。意之所向。辄能善肖其体。昔之读隽永。其文乃如隽永之文。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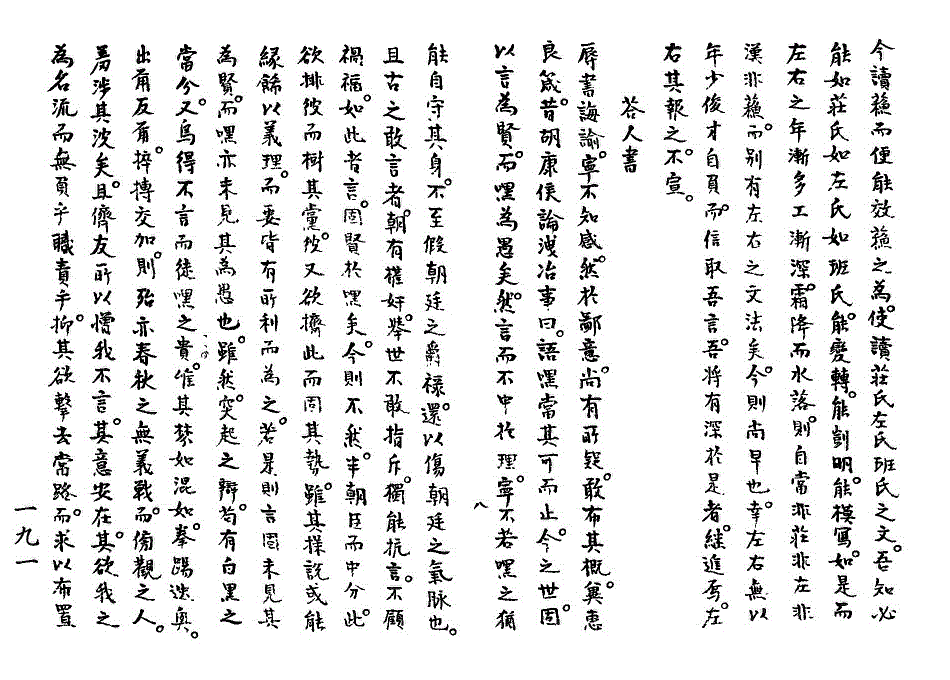 今读苏而便能效苏之为。使读庄氏左氏班氏之文。吾知必能如庄氏如左氏如班氏。能变转。能剀明。能模写。如是而左右之年渐多工渐深。霜降而水落。则自当非庄非左非汉非苏。而别有左右之文法矣。今则尚早也。幸左右无以年少俊才自负。而信取吾言。吾将有深于是者。继进焉。左右其报之。不宣。
今读苏而便能效苏之为。使读庄氏左氏班氏之文。吾知必能如庄氏如左氏如班氏。能变转。能剀明。能模写。如是而左右之年渐多工渐深。霜降而水落。则自当非庄非左非汉非苏。而别有左右之文法矣。今则尚早也。幸左右无以年少俊才自负。而信取吾言。吾将有深于是者。继进焉。左右其报之。不宣。答人书
辱书诲谕。宁不知感。然于鄙意。尚有所疑。敢布其概。冀惠良箴。昔胡康侯论泄冶事曰。语嘿当其可而止。今之世。固以言为贤。而嘿为愚矣。然言而不中于理。宁不若嘿之犹能自守其身。不至假朝廷之爵禄。还以伤朝廷之气脉也。且古之敢言者。朝有权奸。举世不敢指斥。独能抗言。不顾祸福。如此者言。固贤于嘿矣。今则不然。半朝臣而中分。此欲排彼而树其党。彼又欲挤此而固其势。虽其操说或能缘饰以义理。而要皆有所利而为之。若是则言固未见其为贤。而嘿亦未见其为愚也。虽然。突起之辩。苟有白黑之当分。又乌得不言而徒嘿之贵。唯其棼如混如。拳踢迭兴。出尔反尔。捽搏交加。则殆亦春秋之无义战。而傍观之人。羞涉其波矣。且侪友所以憎我不言。其意安在。其欲我之为名流而无负乎职责乎。抑其欲击去当路。而求以布置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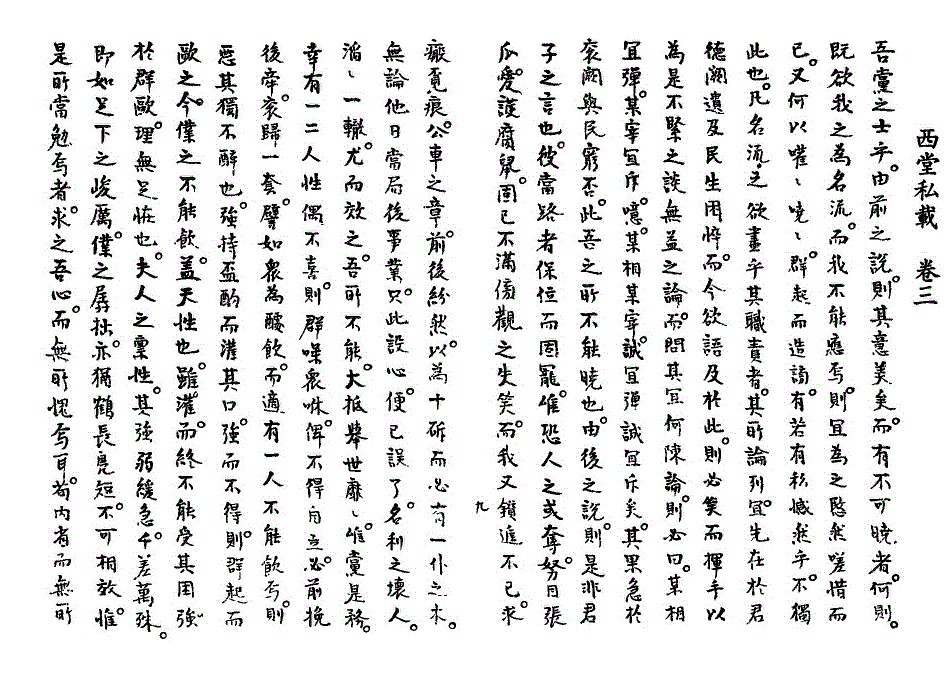 吾党之士乎。由前之说。则其意美矣。而有不可晓者。何则。既欲我之为名流。而我不能应焉。则宜为之悯然嗟惜而已。又何以嚾嚾哓哓。群起而造谤。有若有私憾然乎。不独此也。凡名流之欲尽乎其职责者。其所论列。宜先在于君德阙遗及民生困悴。而今欲语及于此。则必笑而挥手以为是不紧之谈无益之论。而问其宜何陈论。则必曰。某相宜弹。某宰宜斥。噫。某相某宰。诚宜弹诚宜斥矣。其果急于衮阙与民穷否。此吾之所不能晓也。由后之说。则是非君子之言也。彼当路者保位而固宠。唯恐人之或夺。努目张爪。爱护腐鼠。固已不满傍观之失笑。而我又钻进不已。求瘢觅痕。公车之章。前后纷然。以为十斫而必有一仆之木。无论他日当局后事业。只此设心。便已误了。名利之坏人。滔滔一辙。尤而效之。吾所不能。大抵举世靡靡。唯党是务。幸有一二人性偶不喜。则群噪众咻。俾不得自立。必前挽后牵。衮归一套。譬如众为醵饮。而适有一人不能饮焉。则恶其独不醉也。强持杯酌而灌其口。强而不得。则群起而欧之。今仆之不能饮。盖天性也。虽强灌。而终不能受其困于群欧。理无足怪也。夫人之禀性。其强弱缓急。千差万殊。即如足下之峻厉。仆之孱拙。亦犹鹤长凫短。不可相效。惟是所当勉焉者。求之吾心。而无所愧焉耳。苟内省而无所
吾党之士乎。由前之说。则其意美矣。而有不可晓者。何则。既欲我之为名流。而我不能应焉。则宜为之悯然嗟惜而已。又何以嚾嚾哓哓。群起而造谤。有若有私憾然乎。不独此也。凡名流之欲尽乎其职责者。其所论列。宜先在于君德阙遗及民生困悴。而今欲语及于此。则必笑而挥手以为是不紧之谈无益之论。而问其宜何陈论。则必曰。某相宜弹。某宰宜斥。噫。某相某宰。诚宜弹诚宜斥矣。其果急于衮阙与民穷否。此吾之所不能晓也。由后之说。则是非君子之言也。彼当路者保位而固宠。唯恐人之或夺。努目张爪。爱护腐鼠。固已不满傍观之失笑。而我又钻进不已。求瘢觅痕。公车之章。前后纷然。以为十斫而必有一仆之木。无论他日当局后事业。只此设心。便已误了。名利之坏人。滔滔一辙。尤而效之。吾所不能。大抵举世靡靡。唯党是务。幸有一二人性偶不喜。则群噪众咻。俾不得自立。必前挽后牵。衮归一套。譬如众为醵饮。而适有一人不能饮焉。则恶其独不醉也。强持杯酌而灌其口。强而不得。则群起而欧之。今仆之不能饮。盖天性也。虽强灌。而终不能受其困于群欧。理无足怪也。夫人之禀性。其强弱缓急。千差万殊。即如足下之峻厉。仆之孱拙。亦犹鹤长凫短。不可相效。惟是所当勉焉者。求之吾心。而无所愧焉耳。苟内省而无所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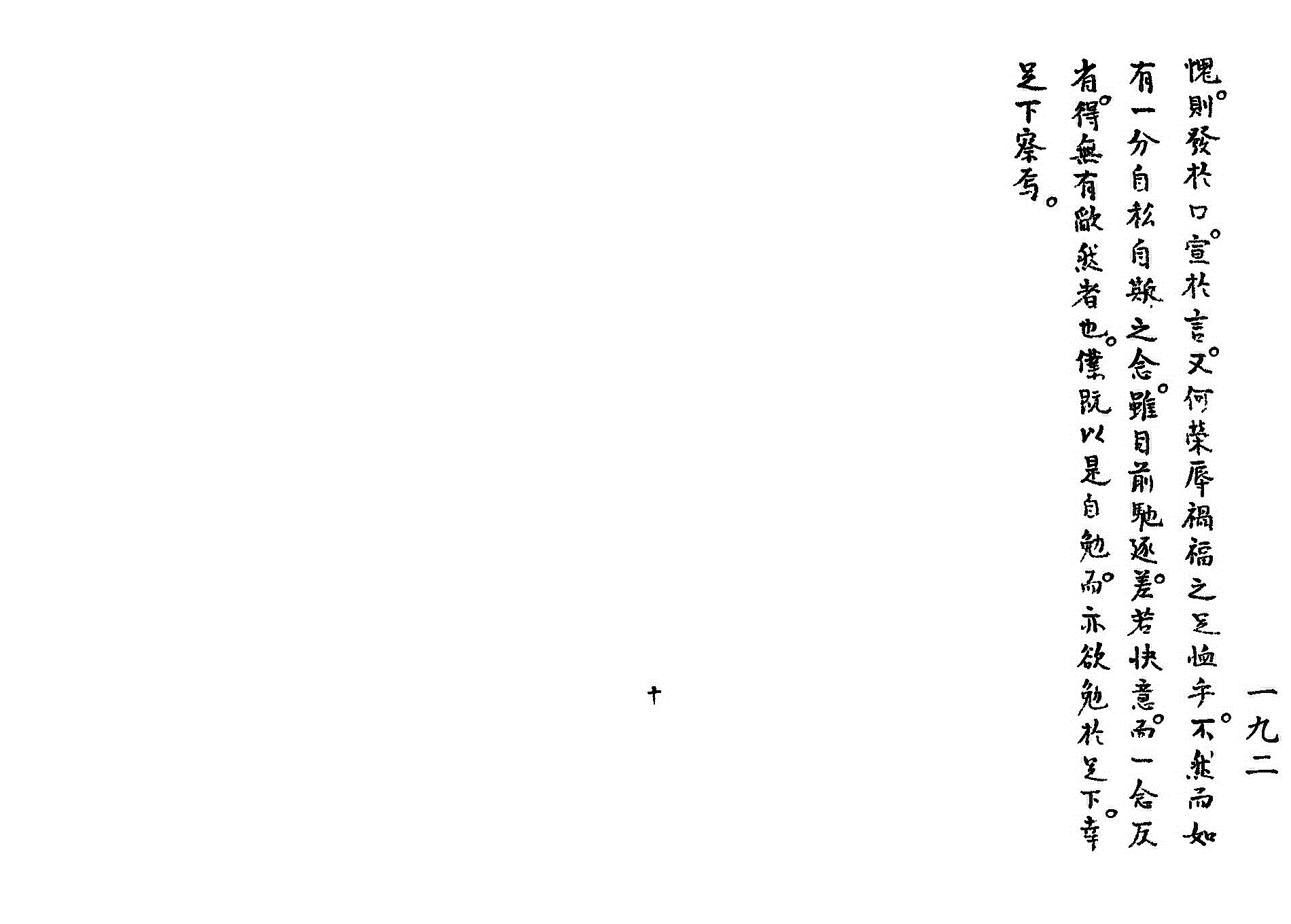 愧。则发于口。宣于言。又何荣辱祸福之足恤乎。不然而如有一分自私自欺之念。虽目前驰逐。差若快意。而一念反省。得无有欿然者也。仆既以是自勉。而亦欲勉于足下。幸足下察焉。
愧。则发于口。宣于言。又何荣辱祸福之足恤乎。不然而如有一分自私自欺之念。虽目前驰逐。差若快意。而一念反省。得无有欿然者也。仆既以是自勉。而亦欲勉于足下。幸足下察焉。西堂私载卷之三
序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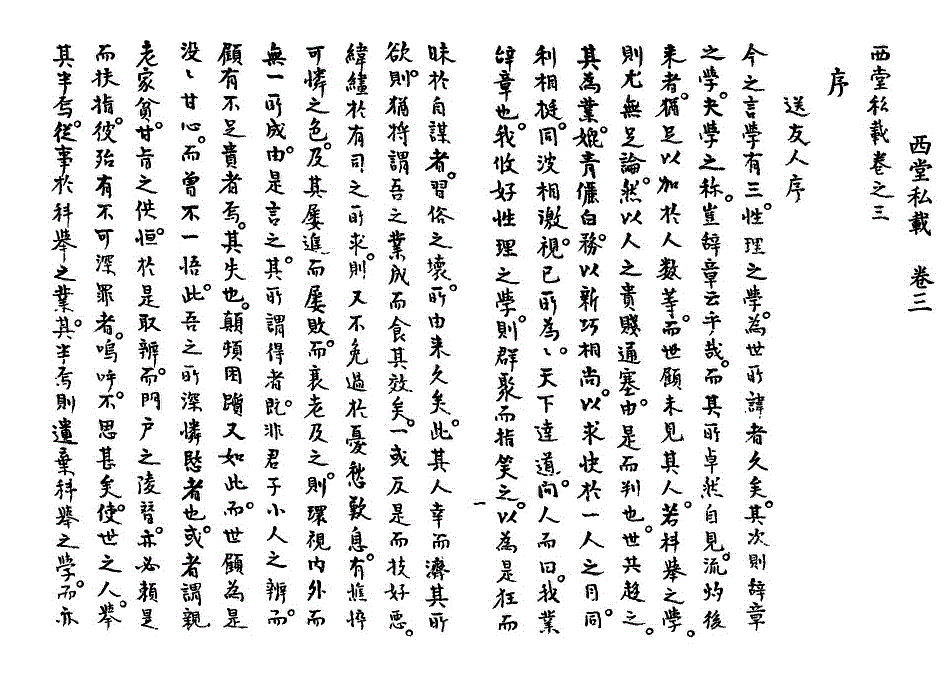 送友人序
送友人序今之言学有三。性理之学。为世所讳者久矣。其次则辞章之学。夫学之称。岂辞章云乎哉。而其所卓然自见。流灼后来者。犹足以加于人数等。而世顾未见其人。若科举之学。则尤无足论。然以人之贵贱通塞。由是而判也。世共趍之。其为业。媲青俪白。务以新巧相尚。以求快于一人之目。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视己所为。为天下达道。问人而曰。我业辞章也。我攸好性理之学。则群聚而指笑之。以为是狂而昧于自谋者。习俗之坏。所由来久矣。此其人幸而济其所欲。则犹将谓吾之业成而食其效矣。一或反是而技好恶。纬繣于有司之所求。则又不免过于忧愁叹息。有憔悴可怜之色。及其屡进而屡败。而衰老及之。则环视内外而无一所成。由是言之。其所谓得者。既非君子小人之辨。而顾有不足贵者焉。其失也。颠顿困踬又如此。而世顾为是没没甘心。而曾不一悟。此吾之所深怜悯者也。或者谓亲老家贫。甘旨之供。恒于是取辨。而门户之陵替。亦必赖是而扶指。彼殆有不可深罪者。呜呼。不思甚矣。使世之人。举其半焉。从事于科举之业。其半焉则遗弃科举之学。而亦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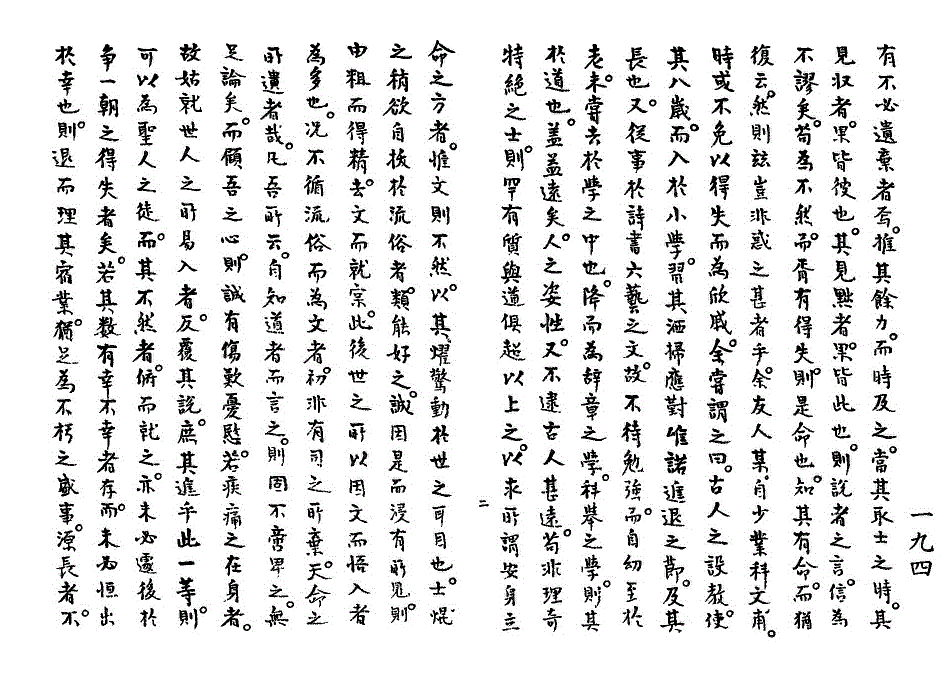 有不必遗弃者焉。推其馀力。而时及之。当其取士之时。其见收者。果皆彼也。其见黜者。果皆此也。则说者之言。信为不谬矣。苟为不然。而胥有得失。则是命也。知其有命。而犹复云。然则玆岂非惑之甚者乎。余友人某甫自少业科文。时或不免以得失而为欣戚。余尝谓之曰。古人之设教。使其八岁。而入于小学。习其洒扫应对唯诺进退之节。及其长也。又从事于诗书六艺之文。故不待勉强。而自幼至于老。未尝去于学之中也。降而为辞章之学。科举之学。则其于道也。盖益远矣。人之姿性。又不逮古人甚远。苟非理奇特绝之士。则罕有质与道俱超以上之。以求所谓安身立命之方者。惟文则不然。以其焜耀惊动于世之耳目也。士之稍欲自拔于流俗者。类能好之。诚因是而浸有所见。则由粗而得精。去文而就实。此后世之所以因文而悟入者为多也。况不循流俗而为文者。初非有司之所弃。天命之所遗者哉。凡吾所云。自知道者而言之。则固不啻卑之。无足论矣。而顾吾之心。则诚有伤叹忧悯。若疾痛之在身者。故姑就世人之所易入者。反覆其说。庶其进乎此一等。则可以为圣人之徒。而其不然者。俯而就之。亦未必遽后于争一朝之得失者矣。若其数有幸不幸者存。而未必恒出于幸也。则退而理其宿业。犹足为不朽之盛事。源长者。不
有不必遗弃者焉。推其馀力。而时及之。当其取士之时。其见收者。果皆彼也。其见黜者。果皆此也。则说者之言。信为不谬矣。苟为不然。而胥有得失。则是命也。知其有命。而犹复云。然则玆岂非惑之甚者乎。余友人某甫自少业科文。时或不免以得失而为欣戚。余尝谓之曰。古人之设教。使其八岁。而入于小学。习其洒扫应对唯诺进退之节。及其长也。又从事于诗书六艺之文。故不待勉强。而自幼至于老。未尝去于学之中也。降而为辞章之学。科举之学。则其于道也。盖益远矣。人之姿性。又不逮古人甚远。苟非理奇特绝之士。则罕有质与道俱超以上之。以求所谓安身立命之方者。惟文则不然。以其焜耀惊动于世之耳目也。士之稍欲自拔于流俗者。类能好之。诚因是而浸有所见。则由粗而得精。去文而就实。此后世之所以因文而悟入者为多也。况不循流俗而为文者。初非有司之所弃。天命之所遗者哉。凡吾所云。自知道者而言之。则固不啻卑之。无足论矣。而顾吾之心。则诚有伤叹忧悯。若疾痛之在身者。故姑就世人之所易入者。反覆其说。庶其进乎此一等。则可以为圣人之徒。而其不然者。俯而就之。亦未必遽后于争一朝之得失者矣。若其数有幸不幸者存。而未必恒出于幸也。则退而理其宿业。犹足为不朽之盛事。源长者。不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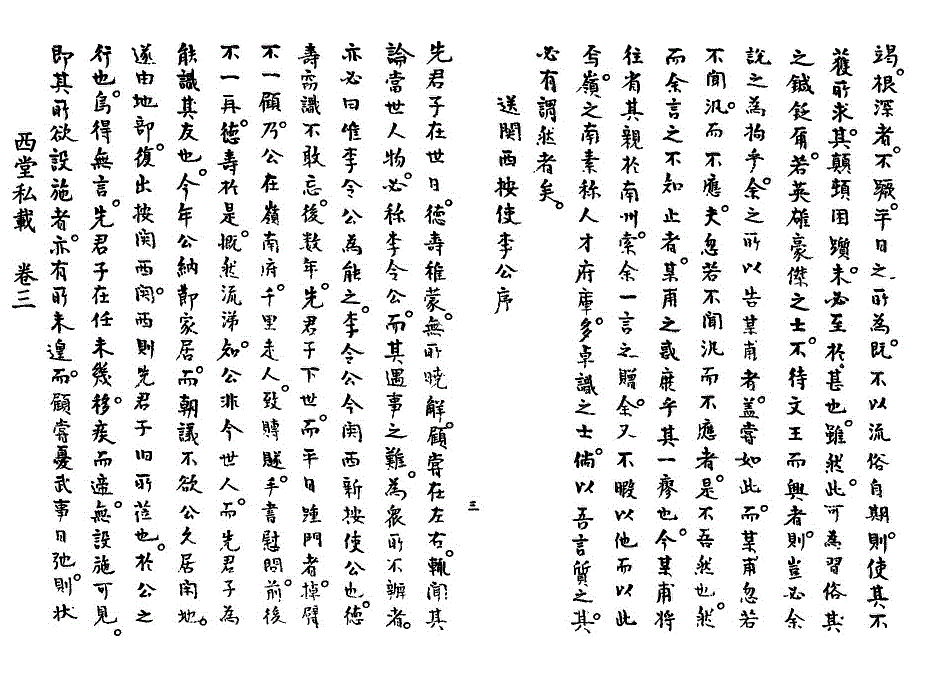 竭。根深者。不蹶。平日之所为。既不以流俗自期。则使其不获所求。其颠顿困踬。未必至于其甚也。虽然。此可为习俗之针𨥧尔。若英雄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则岂必余说之为拘乎。余之所以告某甫者。盖尝如此。而某甫忽若不闻。汎而不应。夫忽若不闻汎而不应者。是不吾然也。然而余言之不知止者。某甫之惑庶乎其一瘳也。今某甫将往省其亲于南州。索余一言之赠。余又不暇以他而以此焉。岭之南素称人才府库。多卓识之士。倘以吾言质之。其必有谓然者矣。
竭。根深者。不蹶。平日之所为。既不以流俗自期。则使其不获所求。其颠顿困踬。未必至于其甚也。虽然。此可为习俗之针𨥧尔。若英雄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则岂必余说之为拘乎。余之所以告某甫者。盖尝如此。而某甫忽若不闻。汎而不应。夫忽若不闻汎而不应者。是不吾然也。然而余言之不知止者。某甫之惑庶乎其一瘳也。今某甫将往省其亲于南州。索余一言之赠。余又不暇以他而以此焉。岭之南素称人才府库。多卓识之士。倘以吾言质之。其必有谓然者矣。送关西按使李公序
先君子在世日。德寿稚蒙。无所晓解。顾尝在左右。辄闻其论当世人物。必称李令公。而其遇事之难。为众所不办者。亦必曰唯李令公为能之。李令公今关西新按使公也。德寿窃识不敢忘。后数年。先君子下世。而平日踵门者。掉臂不一顾。乃公在岭南府。千里走人。致赙𧸙。手书慰问。前后不一再。德寿于是。慨然流涕。知公非今世人。而先君子为能识其友也。今年公纳节家居。而朝议不欲公久居闲地。遂由地部。复出按关西。关西则先君子旧所莅也。于公之行也。乌得无言。先君子在任未几。移疾而遆。无设施可见。即其所欲设施者。亦有所未遑。而顾尝忧武事日弛。则状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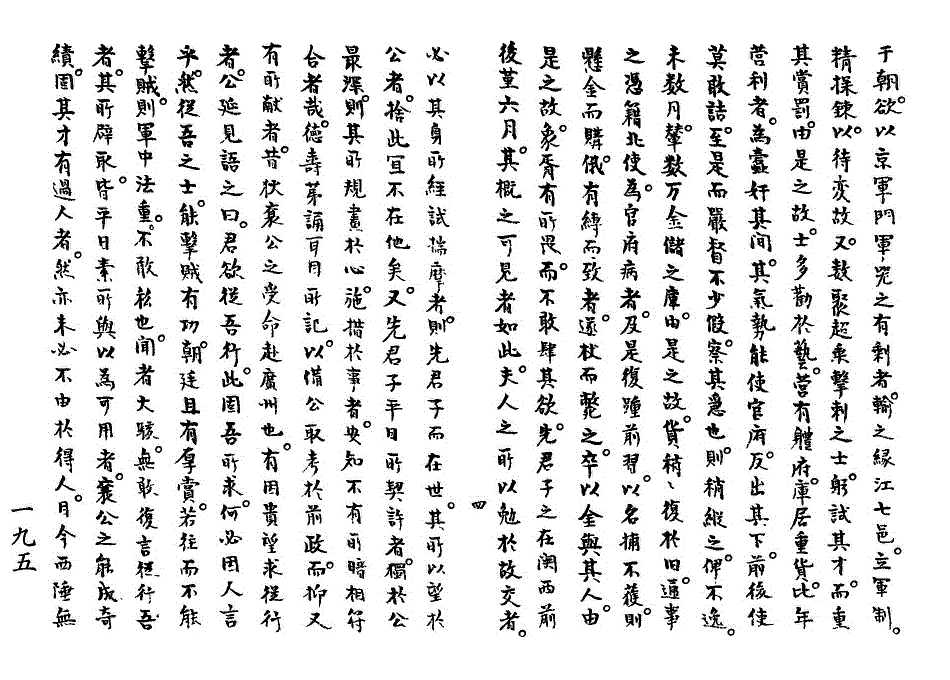 于朝。欲以京军门军器之有剩者。输之缘江七邑。立军制。精操鍊。以待变故。又数聚超乘击刺之士。躬试其才。而重其赏罚。由是之故。士多劝于艺。营有体府。库居重货。比年营利者。为蠹奸其间。其气势能使官府。反出其下。前后使莫敢诘。至是而严督不少假。察其急也。则稍纵之。俾不逸。未数月。辇数万金储之库。由是之故。货稍稍复于旧。通事之凭籍北使。为官府病者。及是复踵前习。以名捕不获。则悬金而购。俄有缚而致者。遂杖而毙之。卒以金与其人。由是之故。象胥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欲。先君子之在关西前后堇六月。其概之可见者如此。夫人之所以勉于故交者。必以其身所经试揣摩者。则先君子而在世。其所以望于公者。舍此宜不在他矣。又先君子平日所契许者。独于公最深。则其所规画于心。施措于事者。安知不有所暗相符合者哉。德寿第诵耳目所记。以备公取考于前政。而抑又有所献者。昔狄襄公之受命赴广州也。有因贵望求从行者。公延见语之曰。君欲从吾行。此固吾所求。何必因人言乎。然从吾之士。能击贼有功。朝廷且有厚赏。若往而不能击贼。则军中法重。吾不敢私也。闻者大骇。无敢复言从行者。其所辟取。皆平日素所与以为可用者。襄公之能成奇绩。固其才有过人者。然亦未必不由于得人。目今西陲无
于朝。欲以京军门军器之有剩者。输之缘江七邑。立军制。精操鍊。以待变故。又数聚超乘击刺之士。躬试其才。而重其赏罚。由是之故。士多劝于艺。营有体府。库居重货。比年营利者。为蠹奸其间。其气势能使官府。反出其下。前后使莫敢诘。至是而严督不少假。察其急也。则稍纵之。俾不逸。未数月。辇数万金储之库。由是之故。货稍稍复于旧。通事之凭籍北使。为官府病者。及是复踵前习。以名捕不获。则悬金而购。俄有缚而致者。遂杖而毙之。卒以金与其人。由是之故。象胥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欲。先君子之在关西前后堇六月。其概之可见者如此。夫人之所以勉于故交者。必以其身所经试揣摩者。则先君子而在世。其所以望于公者。舍此宜不在他矣。又先君子平日所契许者。独于公最深。则其所规画于心。施措于事者。安知不有所暗相符合者哉。德寿第诵耳目所记。以备公取考于前政。而抑又有所献者。昔狄襄公之受命赴广州也。有因贵望求从行者。公延见语之曰。君欲从吾行。此固吾所求。何必因人言乎。然从吾之士。能击贼有功。朝廷且有厚赏。若往而不能击贼。则军中法重。吾不敢私也。闻者大骇。无敢复言从行者。其所辟取。皆平日素所与以为可用者。襄公之能成奇绩。固其才有过人者。然亦未必不由于得人。目今西陲无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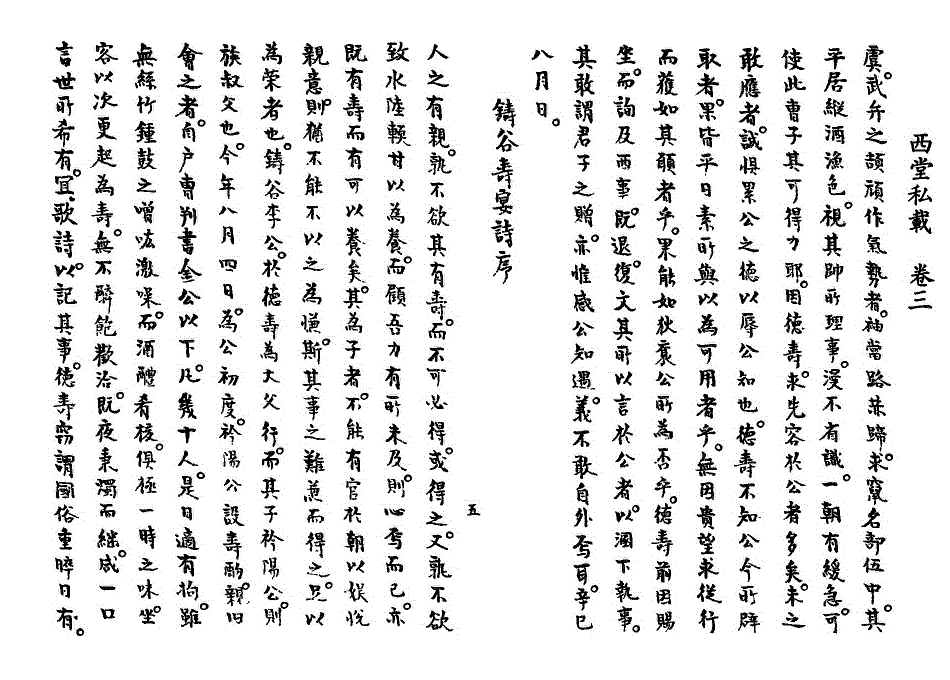 虞。武弁之颉颃作气势者。袖当路赫蹄。求窜名部伍中。其平居纵酒渔色。视其帅所理事。漫不省识。一朝有缓急。可使此曹子其可得力耶。因德寿。求先容于公者多矣。未之敢应者。诚惧累公之德以辱公知也。德寿不知公今所辟取者。果皆平日素所与以为可用者乎。无因贵望求从行而获如其愿者乎。果能如狄襄公所为否乎。德寿前因赐坐。而询及西事。既退。复文其所以言于公者。以溷下执事。其敢谓君子之赠。亦惟感公知遇。义不敢自外焉耳。辛巳八月日。
虞。武弁之颉颃作气势者。袖当路赫蹄。求窜名部伍中。其平居纵酒渔色。视其帅所理事。漫不省识。一朝有缓急。可使此曹子其可得力耶。因德寿。求先容于公者多矣。未之敢应者。诚惧累公之德以辱公知也。德寿不知公今所辟取者。果皆平日素所与以为可用者乎。无因贵望求从行而获如其愿者乎。果能如狄襄公所为否乎。德寿前因赐坐。而询及西事。既退。复文其所以言于公者。以溷下执事。其敢谓君子之赠。亦惟感公知遇。义不敢自外焉耳。辛巳八月日。铸谷寿宴诗序
人之有亲。孰不欲其有寿。而不可必得。或得之。又孰不欲致水陆软甘以为养。而顾吾力有所未及。则心焉而已。亦既有寿而有可以养矣。其为子者。不能有官于朝以娱悦亲意。则犹不能不以之为慊。斯其事之难兼而得之。足以为荣者也。铸谷李公。于德寿为大父行。而其子衿阳公。则族叔父也。今年八月四日。为公初度。衿阳公设寿酌。亲旧会之者。自户曹判书金公以下。凡几十人。是日适有拘。虽无丝竹钟鼓之噌吰激噪。而酒醴肴核。俱极一时之味。坐客以次更起为寿。无不醉饱欢洽。既夜秉烛而继。咸一口言世所希有。宜有歌诗。以记其事。德寿窃谓国俗重晬日。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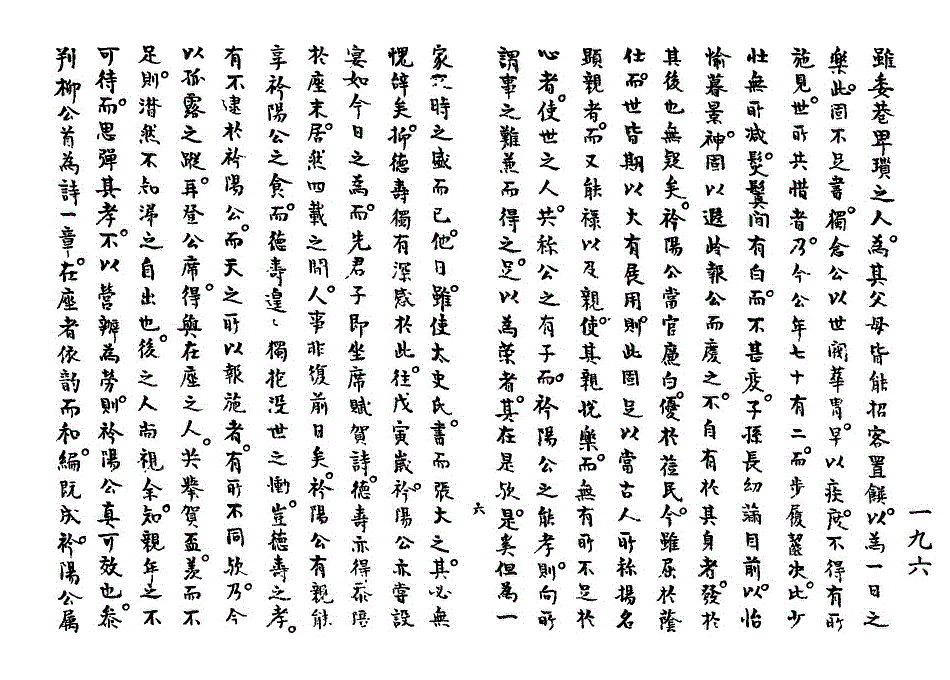 虽委巷卑琐之人。为其父母皆能招客置馔。以为一日之乐。此固不足书。独念公以世阀华胄。早以疾。庶不得有所施见。世所共惜者。乃今公年七十有二。而步履齧决。比少壮无所减。发鬒间有白。而不甚变。子孙长幼满目前。以怡愉暮景。神固以遐龄报公而庆之。不自有于其身者。发于其后也无疑矣。衿阳公当官廉白。优于莅民。今虽屈于荫仕。而世皆期以大有展用。则此固足以当古人所称扬名显亲者。而又能禄以及亲。使其亲悦乐。而无有所不足于心者。使世之人。共称公之有子。而衿阳公之能孝。则向所谓事之难兼而得之。足以为荣者。其在是欤。是奚但为一家之时之盛而已。他日。虽使太史氏。书而张大之。其必无愧辞矣。抑德寿独有深感于此。往戊寅岁。衿阳公亦尝设宴如今日之为。而先君子即坐席赋贺诗。德寿亦得忝陪于座末。居然四载之间。人事非复前日矣。衿阳公有亲能享衿阳公之食。而德寿遑遑独抱没世之恸。岂德寿之孝。有不逮于衿阳公。而天之所以报施者。有所不同欤。乃今以孤露之踪。再登公席。得与在座之人。共举贺杯。羡而不足。则潸然不知涕之自出也。后之人尚视余。知亲年之不可待。而思弹其孝。不以营办为劳。则衿阳公真可效也。参判柳公首为诗一章。在座者依韵而和。编既成。衿阳公属
虽委巷卑琐之人。为其父母皆能招客置馔。以为一日之乐。此固不足书。独念公以世阀华胄。早以疾。庶不得有所施见。世所共惜者。乃今公年七十有二。而步履齧决。比少壮无所减。发鬒间有白。而不甚变。子孙长幼满目前。以怡愉暮景。神固以遐龄报公而庆之。不自有于其身者。发于其后也无疑矣。衿阳公当官廉白。优于莅民。今虽屈于荫仕。而世皆期以大有展用。则此固足以当古人所称扬名显亲者。而又能禄以及亲。使其亲悦乐。而无有所不足于心者。使世之人。共称公之有子。而衿阳公之能孝。则向所谓事之难兼而得之。足以为荣者。其在是欤。是奚但为一家之时之盛而已。他日。虽使太史氏。书而张大之。其必无愧辞矣。抑德寿独有深感于此。往戊寅岁。衿阳公亦尝设宴如今日之为。而先君子即坐席赋贺诗。德寿亦得忝陪于座末。居然四载之间。人事非复前日矣。衿阳公有亲能享衿阳公之食。而德寿遑遑独抱没世之恸。岂德寿之孝。有不逮于衿阳公。而天之所以报施者。有所不同欤。乃今以孤露之踪。再登公席。得与在座之人。共举贺杯。羡而不足。则潸然不知涕之自出也。后之人尚视余。知亲年之不可待。而思弹其孝。不以营办为劳。则衿阳公真可效也。参判柳公首为诗一章。在座者依韵而和。编既成。衿阳公属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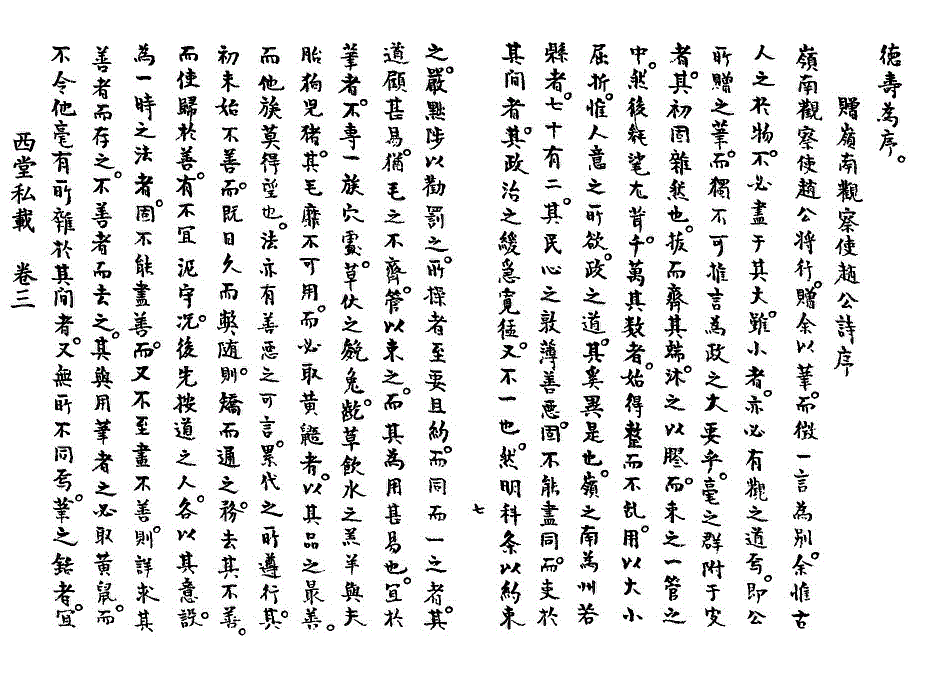 德寿为序。
德寿为序。赠岭南观察使赵公诗序
岭南观察使赵公将行。赠余以笔。而徵一言为别。余惟古人之于物。不必尽于其大。虽小者。亦必有观之道焉。即公所赠之笔。而独不可推言为政之大要乎。毫之群附于皮者。其初固杂然也。拔而齐其端。沐之以胶。而束之一管之中。然后毵㲚尤茸。千万其数者。始得整而不乱。用以大小屈折。惟人意之所欲。政之道。其奚异是也。岭之南为州若县者。七十有二。其民心之敦薄善恶。固不能尽同。而吏于其间者。其政治之缓急宽猛。又不一也。然明科条以约束之。严黜陟以劝罚之。所操者至要且约。而同而一之者。其道顾甚易。犹毛之不齐。管以束之。而其为用甚易也。宜于笔者。不专一族穴处。草伏之㕙兔。龁草饮水之羔羊与夫胎狗儿猪。其毛靡不可用。而必取黄鼯者。以其品之最善。而他族莫得望也。法亦有善恶之可言。累代之所遵行。其初未始不善。而既日久而弊随。则矫而通之。务去其不善。而使归于善。有不宜泥守。况后先按道之人。各以其意。设为一时之法者。固不能尽善。而又不至尽不善。则详求其善者而存之。不善者而去之。其与用笔者之必取黄鼠。而不令他毫有所杂于其间者。又无所不同焉。笔之铦者。宜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7L 页
 于作字而不能寿。其用钝尤不堪钩伸。为治太锐。则作事无渐。而其铓易齾。创是而壹事夫糊涂淹滞焉。则亦岂可哉。是必有中之可执者。凡余所言者。而政之大。亦略可见矣。抑公以笔与余者。以余粗能知属词。而顾余独无以报公哉。公年今向衰。髭发虽少变。而精力尚王。其必享有期颐也。前去六十而当公之寿辰。则余当有侑觞之作。七十而当公之寿辰。则又当有诗若文。七十而致仕。古礼也。况公雅意冲挹。而别业之在湖右者。久擅林麓之胜。公角巾归卧。必有其日。则余尚从诸大夫之后。祖饯上东门外。其供帐车马之盛。与夫路傍咨嗟叹息。如当日疏传之事。余虽无文。犹当书以张大之。以为他日之观。然则公所赠三笔。余当藏之。以俟次第之用。而所以规公与祝公者。于是乎两得其尽矣。既以是副公赠行之须。而复系之以诗云。
于作字而不能寿。其用钝尤不堪钩伸。为治太锐。则作事无渐。而其铓易齾。创是而壹事夫糊涂淹滞焉。则亦岂可哉。是必有中之可执者。凡余所言者。而政之大。亦略可见矣。抑公以笔与余者。以余粗能知属词。而顾余独无以报公哉。公年今向衰。髭发虽少变。而精力尚王。其必享有期颐也。前去六十而当公之寿辰。则余当有侑觞之作。七十而当公之寿辰。则又当有诗若文。七十而致仕。古礼也。况公雅意冲挹。而别业之在湖右者。久擅林麓之胜。公角巾归卧。必有其日。则余尚从诸大夫之后。祖饯上东门外。其供帐车马之盛。与夫路傍咨嗟叹息。如当日疏传之事。余虽无文。犹当书以张大之。以为他日之观。然则公所赠三笔。余当藏之。以俟次第之用。而所以规公与祝公者。于是乎两得其尽矣。既以是副公赠行之须。而复系之以诗云。送岭南按使金公序
余观今世士族家。鲜有孝友之风。唯朋曹是务。而计有毫发利害。则顾于其所薄者。致其款狎。而谇语德色。或施于所厚。甚至同父母昆弟。若昆弟之子。已若路人。虽高门巨阀。世所敀以家风之美者。至其子孙。能遵守而勿失者。少矣。余甚伤焉。惟于今岭南按使金公。则顾常诵而不疑。盖公之曾王考醒斋公。既有忠孝大节。为时闻人。而世载其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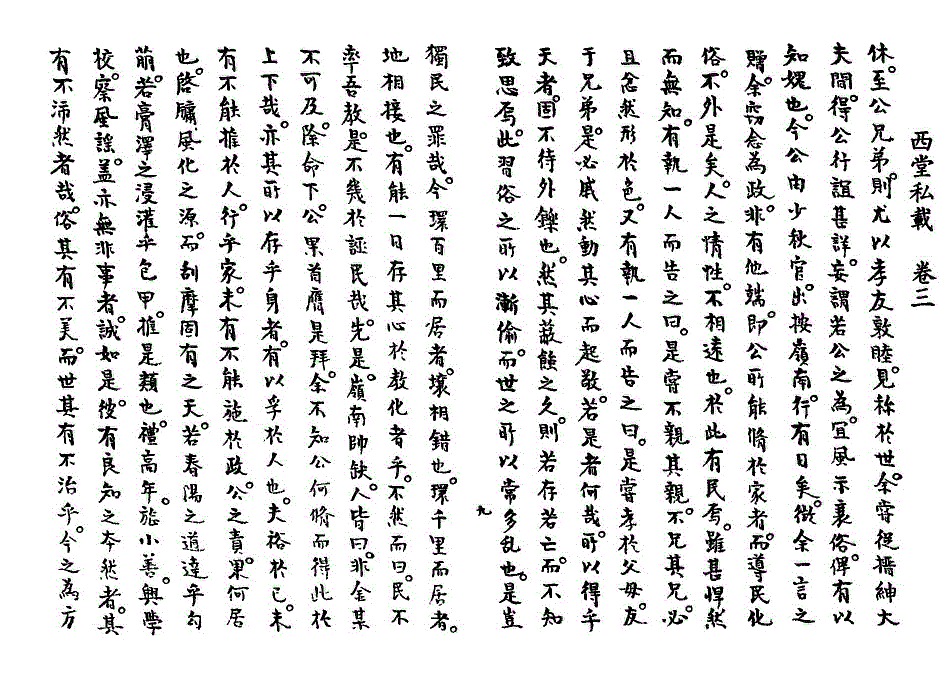 休。至公兄弟。则尤以孝友敦睦。见称于世。余尝从搢绅大夫间。得公行谊甚详。妄谓若公之为。宜风示衰俗。俾有以知愧也。今公由少秋官。出按岭南。行有日矣。徵余一言之赠。余窃念为政。非有他端。即公所能脩于家者。而导民化俗。不外是矣。人之情性。不相远也。于此有民焉。虽甚悍然而无知。有执一人而告之曰。是尝不亲其亲。不兄其兄。必且忿然形于色。又有执一人而告之曰。是尝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必戚然动其心而起敬。若是者何哉。所以得乎天者。固不待外铄也。然其蔽蚀之久。则若存若亡。而不知致思焉。此习俗之所以渐偷。而世之所以常多乱也。是岂独民之罪哉。今环百里而居者。壤相错也。环千里而居者。地相接也。有能一日存其心于教化者乎。不然而曰。民不率吾教。是不几于诬民哉。先是。岭南帅缺。人皆曰。非金某不可及。除命下。公果首膺是拜。余不知公何脩而得此于上下哉。亦其所以存乎身者。有以孚于人也。夫裕于己。未有不能推于人。行乎家。未有不能施于政。公之责。果何居也。启牗风化之源。而刮摩固有之天。若春阳之道达乎勾萌。若膏泽之浸灌乎包甲。推是类也。礼高年。旌小善。兴学校。察风谣。盖亦无非事者。诚如是。彼有良知之本然者。其有不沛然者哉。俗其有不美。而世其有不治乎。今之为方
休。至公兄弟。则尤以孝友敦睦。见称于世。余尝从搢绅大夫间。得公行谊甚详。妄谓若公之为。宜风示衰俗。俾有以知愧也。今公由少秋官。出按岭南。行有日矣。徵余一言之赠。余窃念为政。非有他端。即公所能脩于家者。而导民化俗。不外是矣。人之情性。不相远也。于此有民焉。虽甚悍然而无知。有执一人而告之曰。是尝不亲其亲。不兄其兄。必且忿然形于色。又有执一人而告之曰。是尝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必戚然动其心而起敬。若是者何哉。所以得乎天者。固不待外铄也。然其蔽蚀之久。则若存若亡。而不知致思焉。此习俗之所以渐偷。而世之所以常多乱也。是岂独民之罪哉。今环百里而居者。壤相错也。环千里而居者。地相接也。有能一日存其心于教化者乎。不然而曰。民不率吾教。是不几于诬民哉。先是。岭南帅缺。人皆曰。非金某不可及。除命下。公果首膺是拜。余不知公何脩而得此于上下哉。亦其所以存乎身者。有以孚于人也。夫裕于己。未有不能推于人。行乎家。未有不能施于政。公之责。果何居也。启牗风化之源。而刮摩固有之天。若春阳之道达乎勾萌。若膏泽之浸灌乎包甲。推是类也。礼高年。旌小善。兴学校。察风谣。盖亦无非事者。诚如是。彼有良知之本然者。其有不沛然者哉。俗其有不美。而世其有不治乎。今之为方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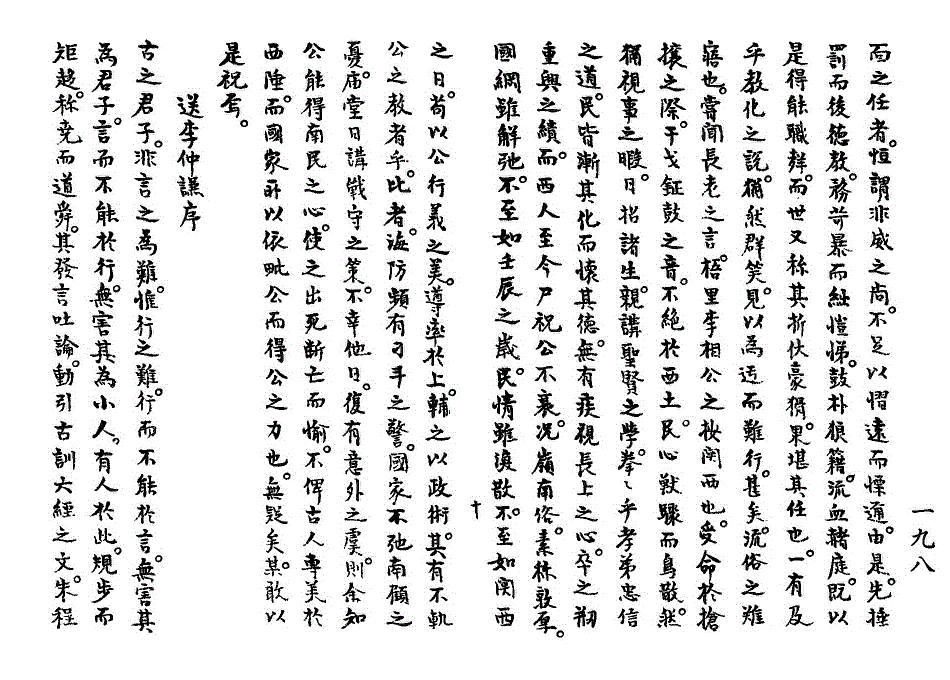 面之任者。恒谓非威之尚。不足以慑远而慄迩。由是。先捶罚而后德教。务苛暴而绌恺悌。鼓朴狼藉。流血赭庭。既以是得能职声。而世又称其折伏豪猾。果堪其任也。一有及乎教化之说。犹然群笑。见以为迂而难行。甚矣。流俗之难寤也。尝闻长老之言。梧里李相公之按关西也。受命于抢攘之际。干戈钲鼓之音。不绝于西土。民心兽骤而鸟散。然犹视事之暇。日招诸生。亲讲圣贤之学。拳拳乎孝弟忠信之道。民皆渐其化而怀其德。无有疾视长上之心。卒之刱重兴之绩。而西人至今尸祝公不衰。况岭南俗。素称敦厚。国纲虽解弛。不至如壬辰之岁。民情虽涣散。不至如关西之日。苟以公行义之美。导率于上。辅之以政术。其有不轨公之教者乎。比者。海防频有刁斗之警。国家不弛南顾之忧。庙堂日讲战守之策。不幸他日。复有意外之虞。则余知公能得南民之心。使之出死断亡而愉。不俾古人专美于西陲。而国家所以依毗公而得公之力也。无疑矣。某敢以是祝焉。
面之任者。恒谓非威之尚。不足以慑远而慄迩。由是。先捶罚而后德教。务苛暴而绌恺悌。鼓朴狼藉。流血赭庭。既以是得能职声。而世又称其折伏豪猾。果堪其任也。一有及乎教化之说。犹然群笑。见以为迂而难行。甚矣。流俗之难寤也。尝闻长老之言。梧里李相公之按关西也。受命于抢攘之际。干戈钲鼓之音。不绝于西土。民心兽骤而鸟散。然犹视事之暇。日招诸生。亲讲圣贤之学。拳拳乎孝弟忠信之道。民皆渐其化而怀其德。无有疾视长上之心。卒之刱重兴之绩。而西人至今尸祝公不衰。况岭南俗。素称敦厚。国纲虽解弛。不至如壬辰之岁。民情虽涣散。不至如关西之日。苟以公行义之美。导率于上。辅之以政术。其有不轨公之教者乎。比者。海防频有刁斗之警。国家不弛南顾之忧。庙堂日讲战守之策。不幸他日。复有意外之虞。则余知公能得南民之心。使之出死断亡而愉。不俾古人专美于西陲。而国家所以依毗公而得公之力也。无疑矣。某敢以是祝焉。送李仲谦序
古之君子。非言之为难。惟行之难。行而不能于言。无害其为君子。言而不能于行。无害其为小人。有人于此。规步而矩趍。称尧而道舜。其发言吐论。动引古训六经之文。朱程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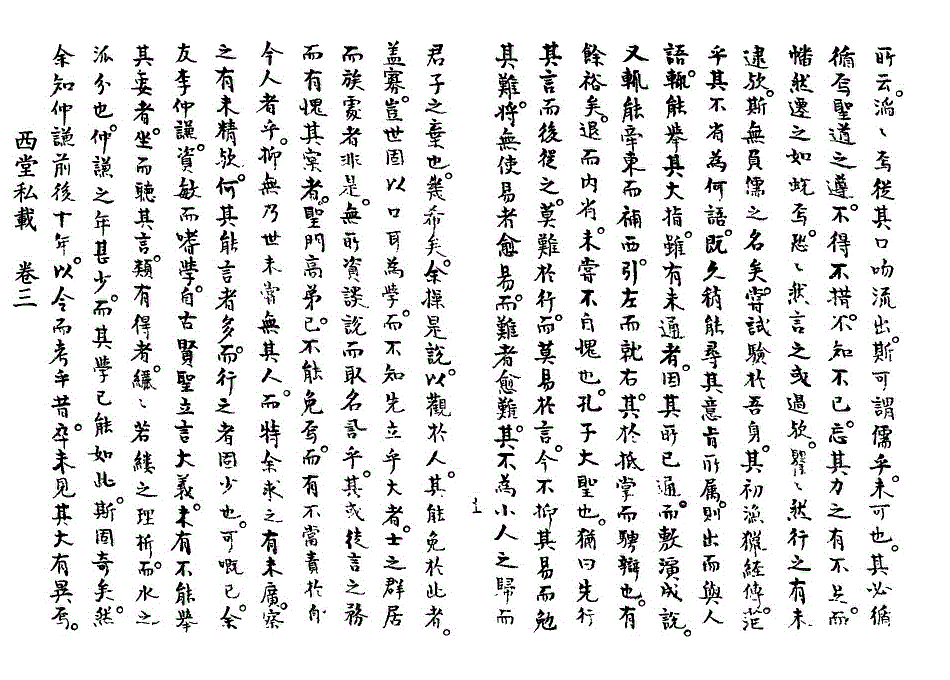 所云。滔滔焉从其口吻流出。斯可谓儒乎。未可也。其必循循焉圣道之遵。不得不措。不知不已。忘其力之有不足。而幡然迁之如蜕焉。恐恐然言之或过欤。瞿瞿然行之有未逮欤。斯无负儒之名矣。尝试验于吾身。其初渔猎经传。茫乎其不省为何语。既久稍能寻其意旨所属。则出而与人语。辄能举其大指。虽有未通者。因其所已通。而敷演成说。又辄能牵东而补西。引左而就右。其于抵掌而骋辩也。有馀裕矣。退而内省。未尝不自愧也。孔子大圣也。犹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莫难于行。而莫易于言。今不抑其易而勉其难。将无使易者愈易。而难者愈难。其不为小人之归而君子之弃也。几希矣。余操是说。以观于人。其能免于此者。盖寡。岂世固以口耳为学。而不知先立乎大者。士之群居而族处者非是。无所资谈说而取名誉乎。其或徒言之务而有愧其实者。自圣门高弟。已不能免焉。而有不当责于今人者乎。抑无乃世未尝无其人。而特余求之有未广。察之有未精欤。何其能言者多。而行之者固少也。可嘅已。余友李仲谦。资敏而嗜学。自古贤圣立言大义。未有不能举其要者。坐而听其言。类有得者。纚纚若缕之理析。而水之派分也。仲谦之年甚少。而其学已能如此。斯固奇矣。然余知仲谦前后十年。以令而考乎昔。卒未见其大有异焉。
所云。滔滔焉从其口吻流出。斯可谓儒乎。未可也。其必循循焉圣道之遵。不得不措。不知不已。忘其力之有不足。而幡然迁之如蜕焉。恐恐然言之或过欤。瞿瞿然行之有未逮欤。斯无负儒之名矣。尝试验于吾身。其初渔猎经传。茫乎其不省为何语。既久稍能寻其意旨所属。则出而与人语。辄能举其大指。虽有未通者。因其所已通。而敷演成说。又辄能牵东而补西。引左而就右。其于抵掌而骋辩也。有馀裕矣。退而内省。未尝不自愧也。孔子大圣也。犹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莫难于行。而莫易于言。今不抑其易而勉其难。将无使易者愈易。而难者愈难。其不为小人之归而君子之弃也。几希矣。余操是说。以观于人。其能免于此者。盖寡。岂世固以口耳为学。而不知先立乎大者。士之群居而族处者非是。无所资谈说而取名誉乎。其或徒言之务而有愧其实者。自圣门高弟。已不能免焉。而有不当责于今人者乎。抑无乃世未尝无其人。而特余求之有未广。察之有未精欤。何其能言者多。而行之者固少也。可嘅已。余友李仲谦。资敏而嗜学。自古贤圣立言大义。未有不能举其要者。坐而听其言。类有得者。纚纚若缕之理析。而水之派分也。仲谦之年甚少。而其学已能如此。斯固奇矣。然余知仲谦前后十年。以令而考乎昔。卒未见其大有异焉。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1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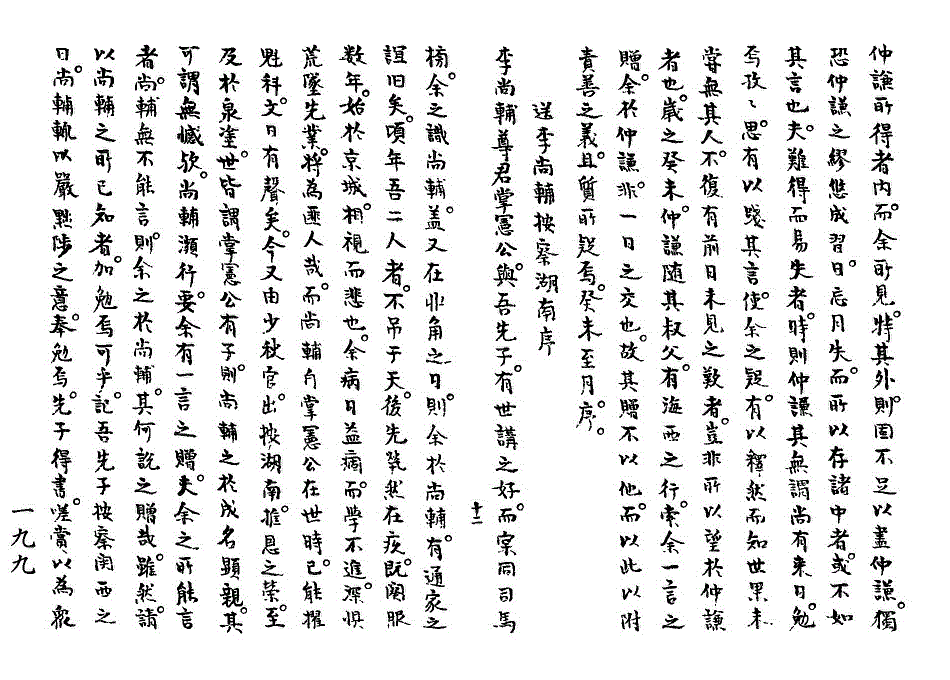 仲谦所得者内。而余所见。特其外。则固不足以尽仲谦。独恐仲谦之缪悠成习。日忘月失。而所以存诸中者。或不如其言也。夫难得而易失者。时则仲谦其无谓尚有来日。勉焉孜孜。思有以践其言。使余之疑。有以释然而知世果未尝无其人。不复有前日未见之叹者。岂非所以望于仲谦者也。岁之癸未。仲谦随其叔父。有海西之行。索余一言之赠。余于仲谦。非一日之交也。故其赠不以他。而以此以附责善之义。且质所疑焉。癸未至月。序。
仲谦所得者内。而余所见。特其外。则固不足以尽仲谦。独恐仲谦之缪悠成习。日忘月失。而所以存诸中者。或不如其言也。夫难得而易失者。时则仲谦其无谓尚有来日。勉焉孜孜。思有以践其言。使余之疑。有以释然而知世果未尝无其人。不复有前日未见之叹者。岂非所以望于仲谦者也。岁之癸未。仲谦随其叔父。有海西之行。索余一言之赠。余于仲谦。非一日之交也。故其赠不以他。而以此以附责善之义。且质所疑焉。癸未至月。序。送李尚辅按察湖南序
李尚辅尊君掌宪公。与吾先子。有世讲之好。而实同司马榜。余之识尚辅。盖又在丱角之日。则余于尚辅。有通家之谊旧矣。顷年吾二人者。不吊于天。后先煢然在疚。既阕服数年。始于京城。相视而悲也。余病日益痼。而学不进。深惧荒坠先业。将为匪人哉。而尚辅自掌宪公在世时。已能擢魁科。文日有声矣。今又由少秋官。出按湖南。推恩之荣。至及于泉涂。世皆谓掌宪公有子。则尚辅之于成名显亲。其可谓无憾欤。尚辅濒行。要余有一言之赠。夫余之所能言者。尚辅无不能言。则余之于尚辅。其何说之赠哉。虽然。请以尚辅之所已知者。加勉焉可乎。记吾先子按察关西之日。尚辅辄以严黜陟之意。奉勉焉。先子得书。嗟赏以为众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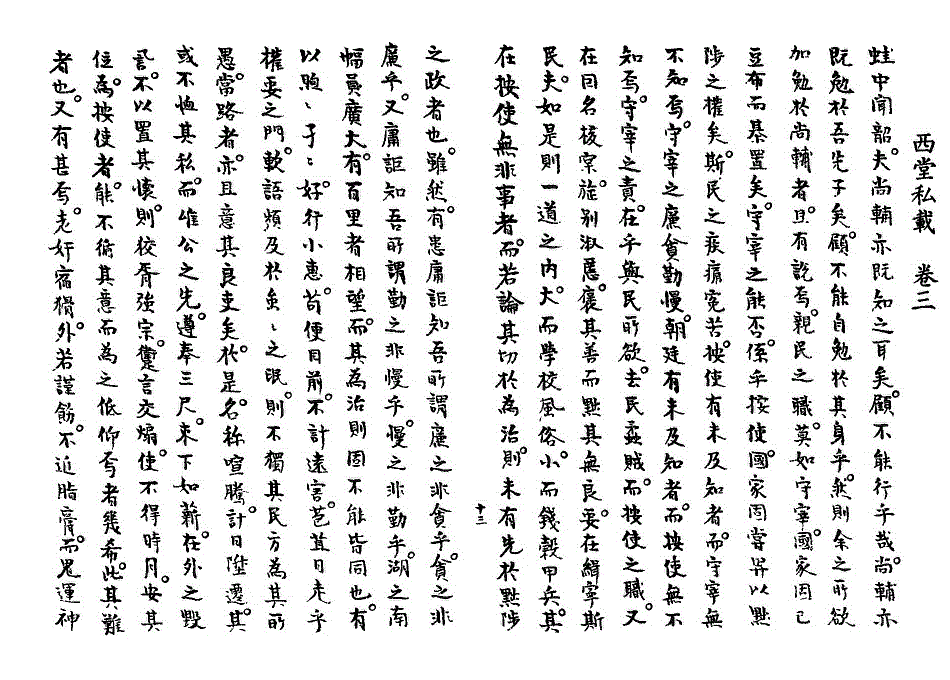 蛙中闻韶。夫尚辅亦既知之耳矣。顾不能行乎哉。尚辅亦既勉于吾先子矣。顾不能自勉于其身乎。然则余之所欲加勉于尚辅者。且有说焉。亲民之职。莫如守宰。国家固已豆布而棋置矣。守宰之能否。系乎按使。国家固尝畀以黜陟之权矣。斯民之疾痛冤苦。按使有未及知者。而守宰无不知焉。守宰之廉贪勤慢。朝廷有未及知者。而按使无不知焉。守宰之责。在乎与民所欲。去民蟊贼。而按使之职。又在因名核实。旌别淑慝。褒其善而黜其无良。要在缉宁斯民。夫如是则一道之内。大而学校风俗。小而钱谷甲兵。其在按使无非事者。而若论其切于为治。则未有先于黜陟之政者也。虽然。有患庸讵知吾所谓廉之非贪乎。贪之非廉乎。又庸讵知吾所谓勤之非慢乎。慢之非勤乎。湖之南幅员广大。有百里者相望。而其为治则固不能皆同也。有以煦煦孑孑。好行小惠。苟便目前。不计远害。苞苴日走乎权要之门。软语频及于蚩蚩之氓。则不独其民方为其所愚。当路者。亦且意其良吏矣。于是。名称喧腾。计日升迁。其或不恤其私。而唯公之先。遵奉三尺。束下如薪。在外之毁誉。不以置其怀。则狡胥强宗。躗言交煽。使不得时月。安其位。为按使者。能不循其意而为之低仰焉者几希。此其难者也。又有甚焉。老奸宿猾。外若谨饬。不近脂膏。而鬼运神
蛙中闻韶。夫尚辅亦既知之耳矣。顾不能行乎哉。尚辅亦既勉于吾先子矣。顾不能自勉于其身乎。然则余之所欲加勉于尚辅者。且有说焉。亲民之职。莫如守宰。国家固已豆布而棋置矣。守宰之能否。系乎按使。国家固尝畀以黜陟之权矣。斯民之疾痛冤苦。按使有未及知者。而守宰无不知焉。守宰之廉贪勤慢。朝廷有未及知者。而按使无不知焉。守宰之责。在乎与民所欲。去民蟊贼。而按使之职。又在因名核实。旌别淑慝。褒其善而黜其无良。要在缉宁斯民。夫如是则一道之内。大而学校风俗。小而钱谷甲兵。其在按使无非事者。而若论其切于为治。则未有先于黜陟之政者也。虽然。有患庸讵知吾所谓廉之非贪乎。贪之非廉乎。又庸讵知吾所谓勤之非慢乎。慢之非勤乎。湖之南幅员广大。有百里者相望。而其为治则固不能皆同也。有以煦煦孑孑。好行小惠。苟便目前。不计远害。苞苴日走乎权要之门。软语频及于蚩蚩之氓。则不独其民方为其所愚。当路者。亦且意其良吏矣。于是。名称喧腾。计日升迁。其或不恤其私。而唯公之先。遵奉三尺。束下如薪。在外之毁誉。不以置其怀。则狡胥强宗。躗言交煽。使不得时月。安其位。为按使者。能不循其意而为之低仰焉者几希。此其难者也。又有甚焉。老奸宿猾。外若谨饬。不近脂膏。而鬼运神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0L 页
 输。满若堵耳。则按使且以为广矣。洁身为吏。毫毛之利。不以自营。而储偫有方。备民之急。则按使且以为贪矣。屑屑焉簿书期会之致察。而以抉摘苛刻为能。则虽其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有不以为勤者乎。高才屈处下邑。不以细故自浼。而初若脱略之为。则虽其大纲克举。而众目随张。有不以为慢者乎。毁誉眩于外。而臧否乱于中。此所以黜陟之难为也。欲其不眩于毁誉。不乱于臧否。则亦在乎察之明而已。处之公而已。察之明。固已十得七八矣。而又处之公。则无不尽也。是惟在尚辅之加之意。尚辅勉乎哉。抑余未冠之年。谒掌宪公于西湖。以诗贽焉。掌宪公谓孺子可教。谬加奖许。后又拜于城南之桃堤。其所以勉诲焉者。视前有加。余今粗能知操觚。而掌宪公已谢世。不获有所就质。今而饰其不腆之文。以道尚辅之行。而其所言。又尚辅所尝奉勉于吾先子者也。虽吾两家屡世之谊。于是焉亦略概见而已。不胜其俛仰人世之感矣。尚辅视此。又当以为如何也。悲夫。丁亥三月。序。
输。满若堵耳。则按使且以为广矣。洁身为吏。毫毛之利。不以自营。而储偫有方。备民之急。则按使且以为贪矣。屑屑焉簿书期会之致察。而以抉摘苛刻为能。则虽其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有不以为勤者乎。高才屈处下邑。不以细故自浼。而初若脱略之为。则虽其大纲克举。而众目随张。有不以为慢者乎。毁誉眩于外。而臧否乱于中。此所以黜陟之难为也。欲其不眩于毁誉。不乱于臧否。则亦在乎察之明而已。处之公而已。察之明。固已十得七八矣。而又处之公。则无不尽也。是惟在尚辅之加之意。尚辅勉乎哉。抑余未冠之年。谒掌宪公于西湖。以诗贽焉。掌宪公谓孺子可教。谬加奖许。后又拜于城南之桃堤。其所以勉诲焉者。视前有加。余今粗能知操觚。而掌宪公已谢世。不获有所就质。今而饰其不腆之文。以道尚辅之行。而其所言。又尚辅所尝奉勉于吾先子者也。虽吾两家屡世之谊。于是焉亦略概见而已。不胜其俛仰人世之感矣。尚辅视此。又当以为如何也。悲夫。丁亥三月。序。送李评事序(台佐)
北路。用武之方也。异时。其马强力善走。其民劲悍耐饥渴。卒然遇猛兽。而能与之格斗。盖其风气然也。比年以来。马之良产绝乏。而士不复可用。此其故何哉。国家许清人岁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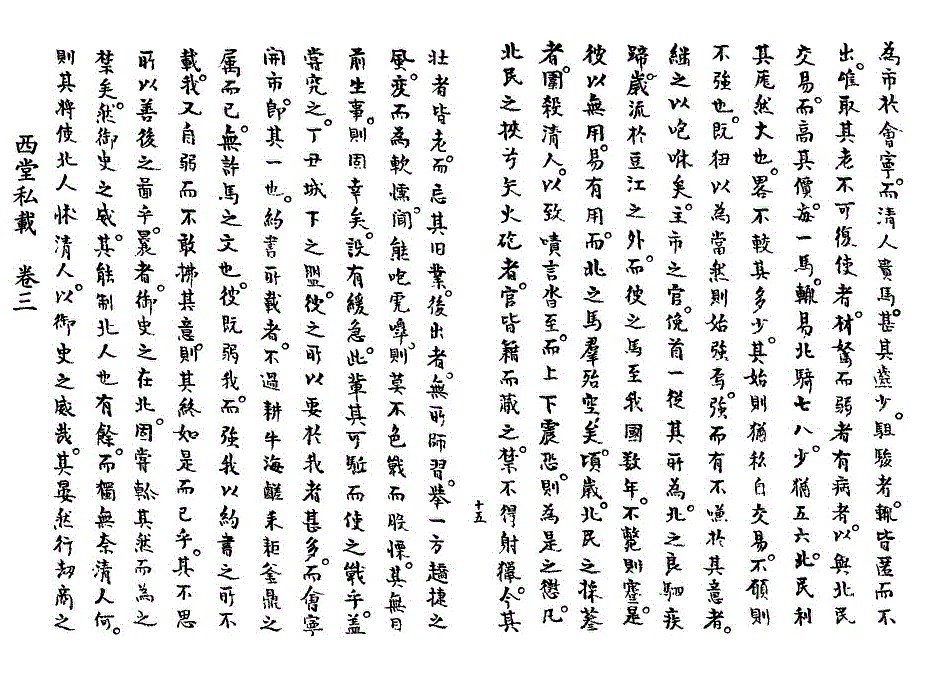 为市于会宁。而清人贵马。甚其齿少。驵骏者。辄皆匿而不出。唯取其老不可复使者。材驽而弱者有病者。以与北民交易。而高其价。每一马。辄易北骑七八。少犹五六。北民利其厖然大也。略不较其多少。其始则犹私自交易。不愿则不强也。既狃以为当然则始强焉。强而有不嗛于其意者。继之以咆咻矣。主市之官。俛首一从其所为。北之良驷疾蹄。岁流于豆江之外。而彼之马至我国数年。不毙则蹇。是彼以无用。易有用。而北之马群殆空矣。顷岁。北民之采蔘者。围杀清人。以致啧言沓至。而上下震恐。则为是之惩。凡北民之挟弓矢火炮者。官皆籍而藏之。禁不得射猎。今其壮者皆老。而忘其旧业。后出者。无所师习。举一方趫捷之风。变而为软懦。闻熊咆虎嗥。则莫不色战而股慄。其无目前生事。则固幸矣。设有缓急。此辈其可驱而使之战乎。盖尝究之。丁丑城下之盟。彼之所以要于我者甚多。而会宁开市。即其一也。约书所载者。不过耕牛海鹾耒耟釜鼎之属而已。无许马之文也。彼既弱我。而强我以约书之所不载。我又自弱而不敢拂其意。则其终如是而已乎。其不思所以善后之啚乎。曩者。御史之在北。固尝轸其然而为之禁矣。然御史之威。其能制北人也有馀。而独无奈清人何。则其将使北人怵清人。以御史之威哉。其晏然行劫商之
为市于会宁。而清人贵马。甚其齿少。驵骏者。辄皆匿而不出。唯取其老不可复使者。材驽而弱者有病者。以与北民交易。而高其价。每一马。辄易北骑七八。少犹五六。北民利其厖然大也。略不较其多少。其始则犹私自交易。不愿则不强也。既狃以为当然则始强焉。强而有不嗛于其意者。继之以咆咻矣。主市之官。俛首一从其所为。北之良驷疾蹄。岁流于豆江之外。而彼之马至我国数年。不毙则蹇。是彼以无用。易有用。而北之马群殆空矣。顷岁。北民之采蔘者。围杀清人。以致啧言沓至。而上下震恐。则为是之惩。凡北民之挟弓矢火炮者。官皆籍而藏之。禁不得射猎。今其壮者皆老。而忘其旧业。后出者。无所师习。举一方趫捷之风。变而为软懦。闻熊咆虎嗥。则莫不色战而股慄。其无目前生事。则固幸矣。设有缓急。此辈其可驱而使之战乎。盖尝究之。丁丑城下之盟。彼之所以要于我者甚多。而会宁开市。即其一也。约书所载者。不过耕牛海鹾耒耟釜鼎之属而已。无许马之文也。彼既弱我。而强我以约书之所不载。我又自弱而不敢拂其意。则其终如是而已乎。其不思所以善后之啚乎。曩者。御史之在北。固尝轸其然而为之禁矣。然御史之威。其能制北人也有馀。而独无奈清人何。则其将使北人怵清人。以御史之威哉。其晏然行劫商之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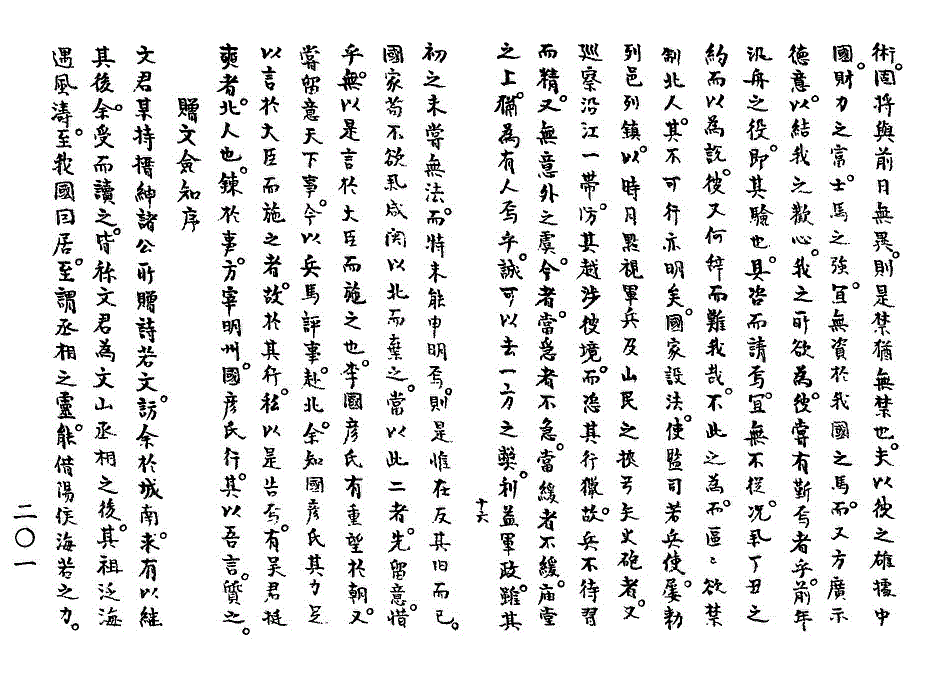 术。固将与前日无异。则是禁犹无禁也。夫以彼之雄据中国。财力之富。士马之强。宜无资于我国之马。而又方广示德意。以结我之欢心。我之所欲为。彼尝有靳焉者乎。前年汎舟之役。即其验也。具咨而请焉。宜无不从。况举丁丑之约而以为说。彼又何辞而难我哉。不此之为。而区区欲禁制北人。其不可行亦明矣。国家设法。使监司若兵使。屡敕列邑列镇。以时月点视军兵及山民之挟弓矢火炮者。又巡察沿江一带。防其越涉彼境。而恣其行猎。故兵不待习而精。又无意外之虞。今者。当急者不急。当缓者不缓。庙堂之上。犹为有人焉乎。诚可以去一方之弊。利益军政。虽其初之未尝无法。而特未能申明焉。则是惟在反其旧而已。国家苟不欲举咸关以北而弃之。当以此二者。先留意。惜乎。无以是言于大臣而施之也。李国彦氏有重望于朝。又尝留意天下事。今以兵马评事。赴北。余知国彦氏其力足以言于大臣而施之者。故于其行。私以是告焉。有吴君挺奭者。北人也。鍊于事。方宰明州。国彦氏行。其以吾言。质之。
术。固将与前日无异。则是禁犹无禁也。夫以彼之雄据中国。财力之富。士马之强。宜无资于我国之马。而又方广示德意。以结我之欢心。我之所欲为。彼尝有靳焉者乎。前年汎舟之役。即其验也。具咨而请焉。宜无不从。况举丁丑之约而以为说。彼又何辞而难我哉。不此之为。而区区欲禁制北人。其不可行亦明矣。国家设法。使监司若兵使。屡敕列邑列镇。以时月点视军兵及山民之挟弓矢火炮者。又巡察沿江一带。防其越涉彼境。而恣其行猎。故兵不待习而精。又无意外之虞。今者。当急者不急。当缓者不缓。庙堂之上。犹为有人焉乎。诚可以去一方之弊。利益军政。虽其初之未尝无法。而特未能申明焉。则是惟在反其旧而已。国家苟不欲举咸关以北而弃之。当以此二者。先留意。惜乎。无以是言于大臣而施之也。李国彦氏有重望于朝。又尝留意天下事。今以兵马评事。赴北。余知国彦氏其力足以言于大臣而施之者。故于其行。私以是告焉。有吴君挺奭者。北人也。鍊于事。方宰明州。国彦氏行。其以吾言。质之。赠文佥知序
文君某持搢绅诸公所赠诗若文。访余于城南。求有以继其后。余受而读之。皆称文君为文山丞相之后。其祖泛海遇风涛。至我国因居。至谓丞相之灵。能借阳侯海若之力。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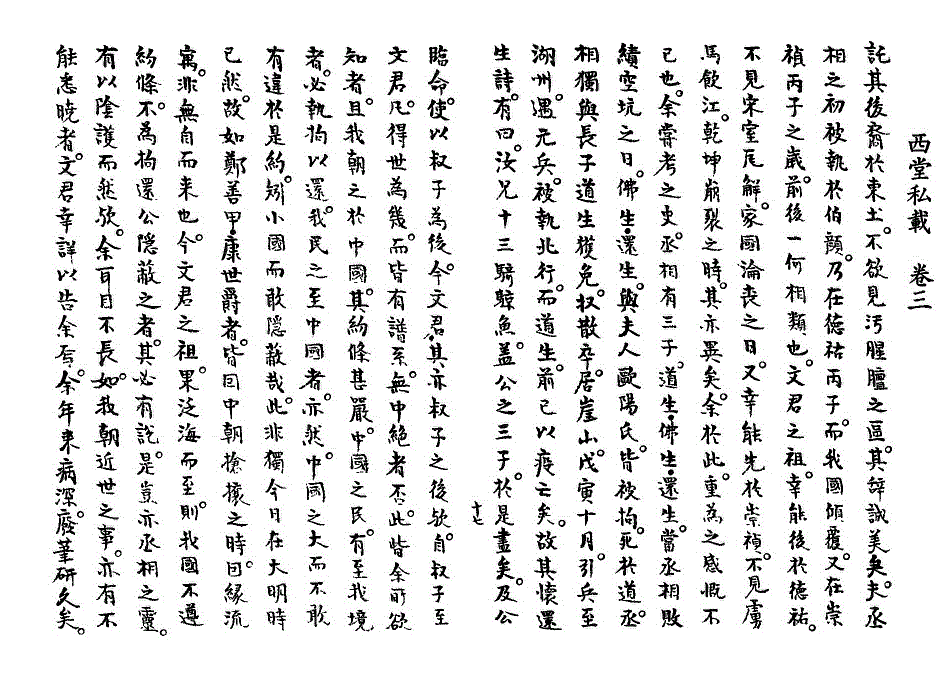 托其后裔于东土。不欲见污腥膻之区。其辞诚美矣。夫丞相之初被执于伯颜。乃在德祐丙子。而我国倾覆。又在崇祯丙子之岁。前后一何相类也。文君之祖。幸能后于德祐。不见宋室瓦解。家国沦丧之日。又幸能先于崇祯。不见虏马饮江。乾坤崩裂之时。其亦异矣。余于此。重为之感慨不已也。余尝考之史。丞相有三子。道生,佛生,还生。当丞相败绩空坑之日。佛生,还生。与夫人欧阳氏。皆被拘。死于道。丞相独与长子道生获免。收散卒。居崖山。戊寅十月。引兵至湖州。遇元兵。被执北行。而道生。前已以疫亡矣。故其怀还生诗。有曰。汝兄十三骑鲸鱼。盖公之三子。于是尽矣。及公临命。使以叔子为后。今文君其亦叔子之后欤。自叔子至文君。凡得世为几。而皆有谱系。无中绝者否。此皆余所欲知者。且我朝之于中国。其约条甚严。中国之民。有至我境者。必执拘以还。我民之至中国者。亦然。中国之大而不敢有违于是约。矧小国而敢隐蔽哉。此非独今日在大明时已然。故如郑善甲,康世爵者。皆因中朝抢攘之时。因缘流寓。非无自而来也。今文君之祖。果泛海而至。则我国不遵约条。不为拘还公隐蔽之者。其必有说。是岂亦丞相之灵。有以阴护而然欤。余耳目不长。如我朝近世之事。亦有不能悉晓者。文君幸详以告余焉。余年来病深。废笔研久矣。
托其后裔于东土。不欲见污腥膻之区。其辞诚美矣。夫丞相之初被执于伯颜。乃在德祐丙子。而我国倾覆。又在崇祯丙子之岁。前后一何相类也。文君之祖。幸能后于德祐。不见宋室瓦解。家国沦丧之日。又幸能先于崇祯。不见虏马饮江。乾坤崩裂之时。其亦异矣。余于此。重为之感慨不已也。余尝考之史。丞相有三子。道生,佛生,还生。当丞相败绩空坑之日。佛生,还生。与夫人欧阳氏。皆被拘。死于道。丞相独与长子道生获免。收散卒。居崖山。戊寅十月。引兵至湖州。遇元兵。被执北行。而道生。前已以疫亡矣。故其怀还生诗。有曰。汝兄十三骑鲸鱼。盖公之三子。于是尽矣。及公临命。使以叔子为后。今文君其亦叔子之后欤。自叔子至文君。凡得世为几。而皆有谱系。无中绝者否。此皆余所欲知者。且我朝之于中国。其约条甚严。中国之民。有至我境者。必执拘以还。我民之至中国者。亦然。中国之大而不敢有违于是约。矧小国而敢隐蔽哉。此非独今日在大明时已然。故如郑善甲,康世爵者。皆因中朝抢攘之时。因缘流寓。非无自而来也。今文君之祖。果泛海而至。则我国不遵约条。不为拘还公隐蔽之者。其必有说。是岂亦丞相之灵。有以阴护而然欤。余耳目不长。如我朝近世之事。亦有不能悉晓者。文君幸详以告余焉。余年来病深。废笔研久矣。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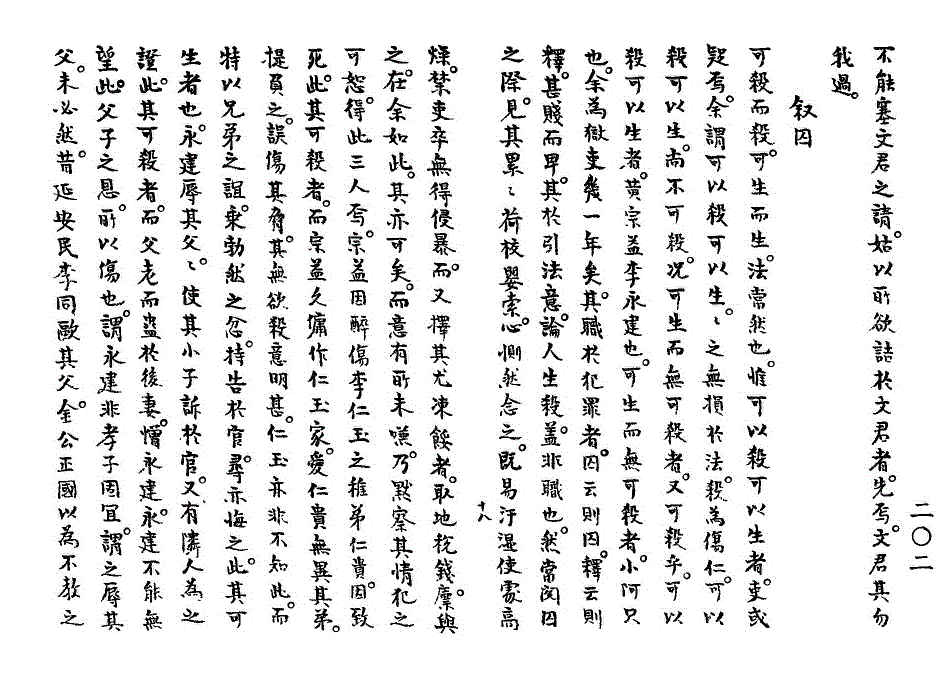 不能塞文君之请。姑以所欲诘于文君者。先焉。文君其勿我过。
不能塞文君之请。姑以所欲诘于文君者。先焉。文君其勿我过。叙囚
可杀而杀。可生而生。法当然也。惟可以杀可以生者。吏或疑焉。余谓可以杀可以生。生之无损于法。杀为伤仁。可以杀可以生。尚不可杀。况可生而无可杀者。又可杀乎。可以杀可以生者。黄宗益李永建也。可生而无可杀者。小阿只也。余为狱吏几一年矣。其职于犯罪者。囚云则囚。释云则释。甚贱而卑。其于引法意。论人生杀。盖非职也。然当阅囚之际。见其累累荷校婴索。心恻然念之。既易污湿使处高燥。禁吏卒无得侵暴。而又择其尤冻馁者。取地税钱。廪与之。在余如此。其亦可矣。而意有所未嗛。乃默察其情犯之可恕。得此三人焉。宗益因醉伤李仁玉之稚弟仁贵。因致死。此其可杀者。而宗益久佣作仁玉家。爱仁贵无异其弟。提负之。误伤其胁。其无欲杀意明甚。仁玉亦非不知此。而特以兄弟之谊。乘勃然之忿。持告于官。寻亦悔之。此其可生者也。永建辱其父。父使其小子诉于官。又有邻人为之證。此其可杀者。而父老而蛊于后妻。憎永建。永建不能无望。此父子之恩。所以伤也。谓永建非孝子固宜。谓之辱其父。未必然。昔延安民李同欧其父。金公正国以为不教之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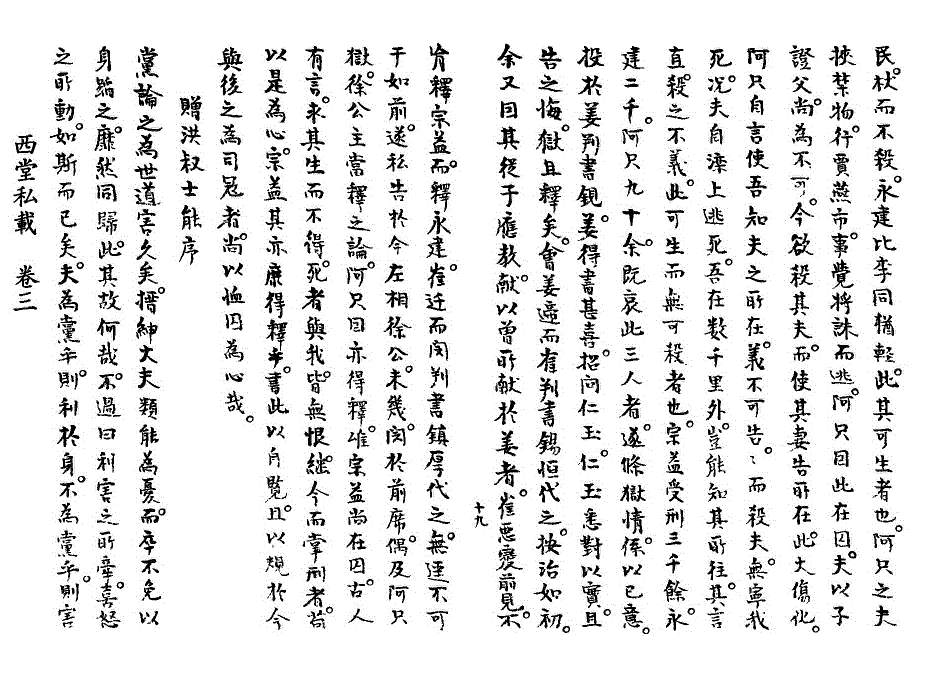 民。杖而不杀。永建比李同犹轻。此其可生者也。阿只之夫挟禁物。行贾燕市。事觉将诛而逃。阿只因此在囚。夫以子證父。尚为不可。今欲杀其夫。而使其妻告所在。此大伤化。阿只自言使吾知夫之所在。义不可告。告而杀夫。无宁我死。况夫自滦上逃死。吾在数千里外。岂能知其所往。其言直。杀之不义。此可生而无可杀者也。宗益受刑三千馀。永建二千。阿只九十。余既哀此三人者。遂条狱情。系以己意。投于姜判书鋧。姜得书甚喜。招问仁玉。仁玉悉对以实。且告之悔。狱且释矣。会姜遆而崔判书锡恒代之。按治如初。余又因其从于应教。献以曾所献于姜者。崔恶变前见。不肯释宗益。而释永建。崔迁而闵判书镇厚代之。无径不可干如前。遂私告于今左相徐公。未几。闵于前席。偶及阿只狱。徐公主当释之论。阿只因亦得释。唯宗益尚在囚。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死者与我。皆无恨。继今而掌刑者。苟以是为心。宗益其亦庶得释乎。书此以自览。且以规于今与后之为司寇者。尚以恤囚为心哉。
民。杖而不杀。永建比李同犹轻。此其可生者也。阿只之夫挟禁物。行贾燕市。事觉将诛而逃。阿只因此在囚。夫以子證父。尚为不可。今欲杀其夫。而使其妻告所在。此大伤化。阿只自言使吾知夫之所在。义不可告。告而杀夫。无宁我死。况夫自滦上逃死。吾在数千里外。岂能知其所往。其言直。杀之不义。此可生而无可杀者也。宗益受刑三千馀。永建二千。阿只九十。余既哀此三人者。遂条狱情。系以己意。投于姜判书鋧。姜得书甚喜。招问仁玉。仁玉悉对以实。且告之悔。狱且释矣。会姜遆而崔判书锡恒代之。按治如初。余又因其从于应教。献以曾所献于姜者。崔恶变前见。不肯释宗益。而释永建。崔迁而闵判书镇厚代之。无径不可干如前。遂私告于今左相徐公。未几。闵于前席。偶及阿只狱。徐公主当释之论。阿只因亦得释。唯宗益尚在囚。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死者与我。皆无恨。继今而掌刑者。苟以是为心。宗益其亦庶得释乎。书此以自览。且以规于今与后之为司寇者。尚以恤囚为心哉。赠洪叔士能序
党论之为世道害久矣。搢绅大夫类能为忧。而卒不免以身蹈之。靡然同归。此其故何哉。不过曰利害之所牵。喜怒之所动。如斯而已矣。夫为党乎。则利于身。不为党乎。则害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3L 页
 于身。人之情安得不舍其害于身者。而趣其利于身者也。为吾党乎。则其人可喜。不为吾党乎。则其人可怒。人之情安得不进其所可喜者。而挤其所可怒者也。由是之故。党论日炽。而其能有所树立于其间者鲜焉。可不为之太息乎。然则士君子出身而仕于朝。固不免于为党矣。其将奚党之党而为可哉。党乎臧乎。臧未必尽是也。党乎谷乎。谷未必尽是也。不党乎臧。不党乎谷。而中之立乎。是子莫之执中也。不党乎臧。不党乎谷。不为中之立。而无是无非。瞋瞋如新生之犊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若是者。是无是非之心者也。不可谓之人矣。若然者。其将奚党之党而为可哉。亦曰。不党乎臧。不党乎谷。不为中之立。不为无是非之论。而唯心与口之相应而已矣。心与口不相应者。盖滔滔于世也。论出于谷臧之心。未必非也。而口则非之。论出于臧谷之心。未必非也。而口则非之。论出于臧谷之同党。则其心未必以为是也。而其口则必以为是焉者。臧谷又同然。此之谓心与口不相应也。若夫心与口相应者则不然。是者是之。不问臧与谷也。非者非之。不问臧与谷也。其心是之。则其口亦是之。其心非之。则其口亦非之。不谋于党而谋于心。不听乎党。而听乎心。心既然矣。而口亦然。此之谓心与口相应之论也。夫心是吾心。口是吾口。苟心与口。不
于身。人之情安得不舍其害于身者。而趣其利于身者也。为吾党乎。则其人可喜。不为吾党乎。则其人可怒。人之情安得不进其所可喜者。而挤其所可怒者也。由是之故。党论日炽。而其能有所树立于其间者鲜焉。可不为之太息乎。然则士君子出身而仕于朝。固不免于为党矣。其将奚党之党而为可哉。党乎臧乎。臧未必尽是也。党乎谷乎。谷未必尽是也。不党乎臧。不党乎谷。而中之立乎。是子莫之执中也。不党乎臧。不党乎谷。不为中之立。而无是无非。瞋瞋如新生之犊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若是者。是无是非之心者也。不可谓之人矣。若然者。其将奚党之党而为可哉。亦曰。不党乎臧。不党乎谷。不为中之立。不为无是非之论。而唯心与口之相应而已矣。心与口不相应者。盖滔滔于世也。论出于谷臧之心。未必非也。而口则非之。论出于臧谷之心。未必非也。而口则非之。论出于臧谷之同党。则其心未必以为是也。而其口则必以为是焉者。臧谷又同然。此之谓心与口不相应也。若夫心与口相应者则不然。是者是之。不问臧与谷也。非者非之。不问臧与谷也。其心是之。则其口亦是之。其心非之。则其口亦非之。不谋于党而谋于心。不听乎党。而听乎心。心既然矣。而口亦然。此之谓心与口相应之论也。夫心是吾心。口是吾口。苟心与口。不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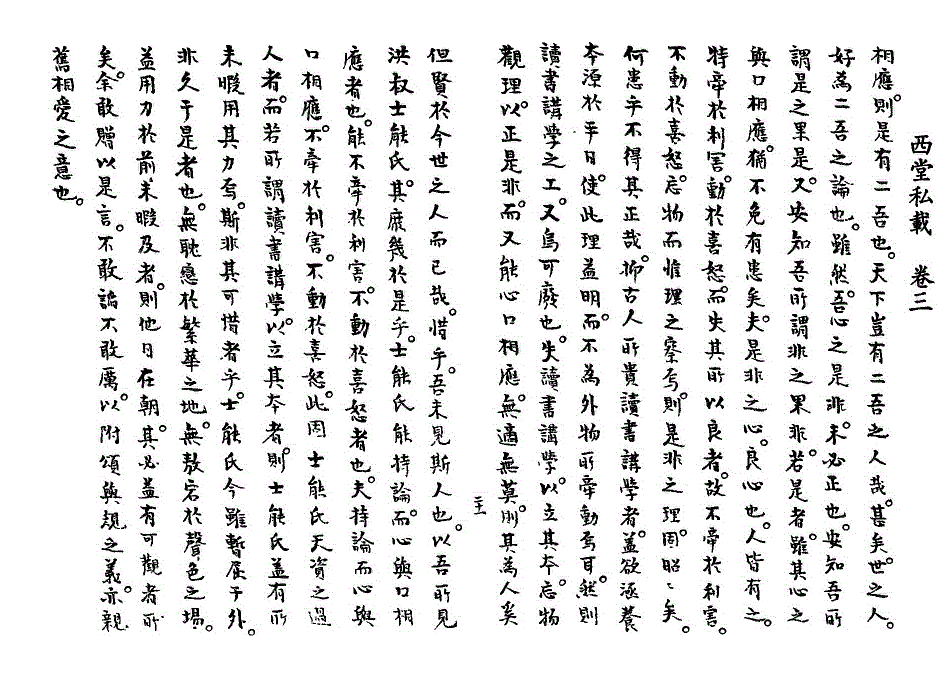 相应。则是有二吾也。天下岂有二吾之人哉。甚矣。世之人。好为二吾之论也。虽然。吾心之是非。未必正也。安知吾所谓是之果是。又安知吾所谓非之果非。若是者。虽其心之与口相应。犹不免有患矣。夫是非之心。良心也。人皆有之。特牵于利害。动于喜怒。而失其所以良者。故不牵于利害。不动于喜怒。忘物而惟理之察焉。则是非之理。固昭昭矣。何患乎不得其正哉。抑古人所贵读书讲学者。盖欲涵养本源于平日。使此理益明。而不为外物所牵动焉耳。然则读书讲学之工。又乌可废也。失读书讲学。以立其本。忘物观理。以正是非。而又能心口相应。无适无莫。则其为人奚但贤于今世之人而已哉。惜乎。吾未见斯人也。以吾所见洪叔士能氏。其庶几于是乎。士能氏能持论。而心与口相应者也。能不牵于利害。不动于喜怒者也。夫持论而心与口相应。不牵于利害。不动于喜怒。此固士能氏天资之过人者。而若所谓读书讲学。以立其本者。则士能氏盖有所未暇用其力焉。斯非其可惜者乎。士能氏今虽暂屈于外。非久于是者也。无耽恋于繁华之地。无敖宕于声色之场。益用力于前所未暇及者。则他日在朝。其必益有可观者矣。余敢赠以是言。不敢谄不敢厉。以附颂与规之义。亦亲旧相爱之意也。
相应。则是有二吾也。天下岂有二吾之人哉。甚矣。世之人。好为二吾之论也。虽然。吾心之是非。未必正也。安知吾所谓是之果是。又安知吾所谓非之果非。若是者。虽其心之与口相应。犹不免有患矣。夫是非之心。良心也。人皆有之。特牵于利害。动于喜怒。而失其所以良者。故不牵于利害。不动于喜怒。忘物而惟理之察焉。则是非之理。固昭昭矣。何患乎不得其正哉。抑古人所贵读书讲学者。盖欲涵养本源于平日。使此理益明。而不为外物所牵动焉耳。然则读书讲学之工。又乌可废也。失读书讲学。以立其本。忘物观理。以正是非。而又能心口相应。无适无莫。则其为人奚但贤于今世之人而已哉。惜乎。吾未见斯人也。以吾所见洪叔士能氏。其庶几于是乎。士能氏能持论。而心与口相应者也。能不牵于利害。不动于喜怒者也。夫持论而心与口相应。不牵于利害。不动于喜怒。此固士能氏天资之过人者。而若所谓读书讲学。以立其本者。则士能氏盖有所未暇用其力焉。斯非其可惜者乎。士能氏今虽暂屈于外。非久于是者也。无耽恋于繁华之地。无敖宕于声色之场。益用力于前所未暇及者。则他日在朝。其必益有可观者矣。余敢赠以是言。不敢谄不敢厉。以附颂与规之义。亦亲旧相爱之意也。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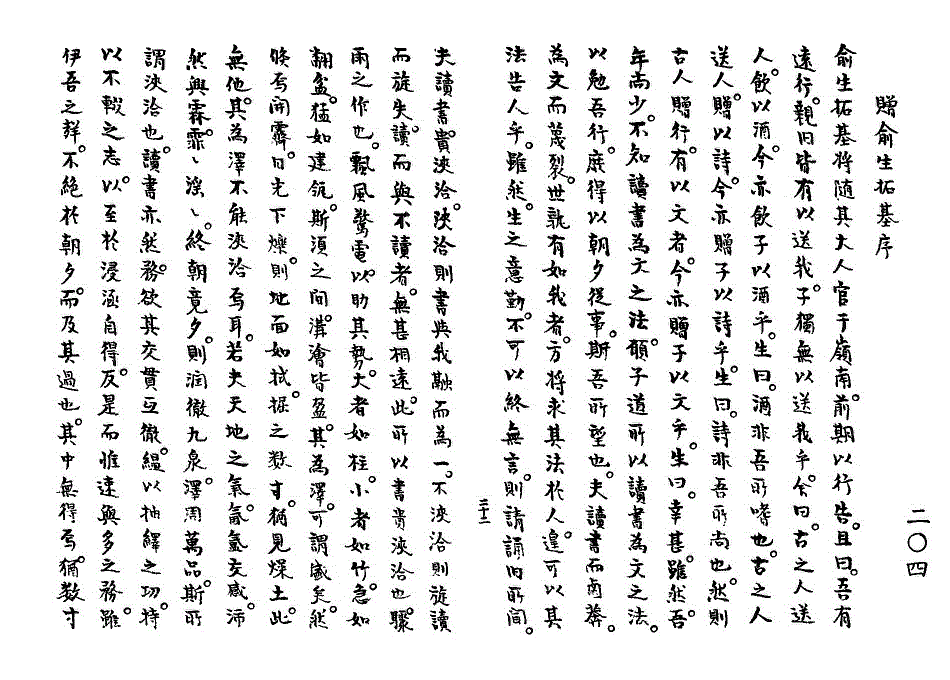 赠俞生拓基序
赠俞生拓基序俞生拓基将随其大人官于岭南。前期以行告。且曰。吾有远行。亲旧皆有以送我。子独无以送我乎。余曰。古之人送人。饮以酒。今亦饮子以酒乎。生曰。酒非吾所嗜也。古之人送人。赠以诗。今亦赠子以诗乎。生曰。诗非吾所尚也。然则古人赠行。有以文者。今亦赠子以文乎。生曰。幸甚。虽然。吾年尚少。不知读书为文之法。愿子道所以读书为文之法。以勉吾行。庶得以朝夕从事。斯吾所望也。夫读书而卤莽。为文而蔑裂。世孰有如我者。方将求其法于人。遑可以其法告人乎。虽然。生之意勤。不可以终无言。则请诵旧所闻。夫读书。贵浃洽。浃洽则书与我融而为一。不浃洽则旋读而旋失。读而与不读者。无甚相远。此所以书贵浃洽也。骤雨之作也。飘风惊电。以助其势。大者如柱。小者如竹。急如翻盆。猛如建瓴。斯须之间。沟浍皆盈。其为泽。可谓盛矣。然倏焉开霁。日光下烁。则地面如拭。掘之数寸。犹见燥土。此无他。其为泽不能浃洽焉耳。若夫天地之气。氤氲交感。沛然兴霖。霏霏淫淫。终朝竟夕。则润彻九泉。泽周万品。斯所谓浃洽也。读书亦然。务欲其交贯互彻。缊以抽绎之功。持以不辍之志。以至于浸涵自得。反是而惟速与多之务。虽伊吾之声。不绝于朝夕。而及其过也。其中无得焉。犹数寸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5H 页
 之外。尚为燥土。甚可戒也。浃洽有道。精斯浃洽矣。未有精而不浃洽者。不精亦未有能浃洽者也。是故。欲浃洽。当求其精。其读古人文。其意以为人之为言。固当如是也者。虽其自为文。其为言亦固当如是也者。吾之意与古人之言。相安相适。而无相迕相拂者焉。苟不然则必其言有不合于理者也。又不然则必吾之知与见。有不逮于古人者也。又不然则必其有残编错句者也。与之反覆焉。与之磨戛焉。久则昭昭然。白黑分矣。斯所谓精也。斯所谓精之至也。如是而下笔。有不沛然者乎。虽然。有患一任其滔滔莽莽。则其失也流于靡。为是之虑。而章揣句模。则其失也流于局。局与靡。皆文之忌也。纵而无至于放。法而无至于拘。使气贯乎一篇。而法行乎句节之际。斯善矣。两阵相望。阗然鼓之。挥刃贾勇。前突坚垒。其气若不可御者。而犹尚曰三步四步而止齐。五步六步而止齐。此固用兵之法。而亦可喻于文者也。夫为文之工。由乎读书之浃洽。读书之浃洽。由乎读书之精。苟精则浃洽矣。浃洽则下笔而无滞矣。生果能率由是道以求之。生之为文。不忧不如古人矣。
之外。尚为燥土。甚可戒也。浃洽有道。精斯浃洽矣。未有精而不浃洽者。不精亦未有能浃洽者也。是故。欲浃洽。当求其精。其读古人文。其意以为人之为言。固当如是也者。虽其自为文。其为言亦固当如是也者。吾之意与古人之言。相安相适。而无相迕相拂者焉。苟不然则必其言有不合于理者也。又不然则必吾之知与见。有不逮于古人者也。又不然则必其有残编错句者也。与之反覆焉。与之磨戛焉。久则昭昭然。白黑分矣。斯所谓精也。斯所谓精之至也。如是而下笔。有不沛然者乎。虽然。有患一任其滔滔莽莽。则其失也流于靡。为是之虑。而章揣句模。则其失也流于局。局与靡。皆文之忌也。纵而无至于放。法而无至于拘。使气贯乎一篇。而法行乎句节之际。斯善矣。两阵相望。阗然鼓之。挥刃贾勇。前突坚垒。其气若不可御者。而犹尚曰三步四步而止齐。五步六步而止齐。此固用兵之法。而亦可喻于文者也。夫为文之工。由乎读书之浃洽。读书之浃洽。由乎读书之精。苟精则浃洽矣。浃洽则下笔而无滞矣。生果能率由是道以求之。生之为文。不忧不如古人矣。送冬至书状官韩锡甫序
国家设官府。皆置吏胥。交异国。各有译胥。所以掌文书而通情志也。然舞文驭智之吏。能眩幻是非。颠倒曲直。以笼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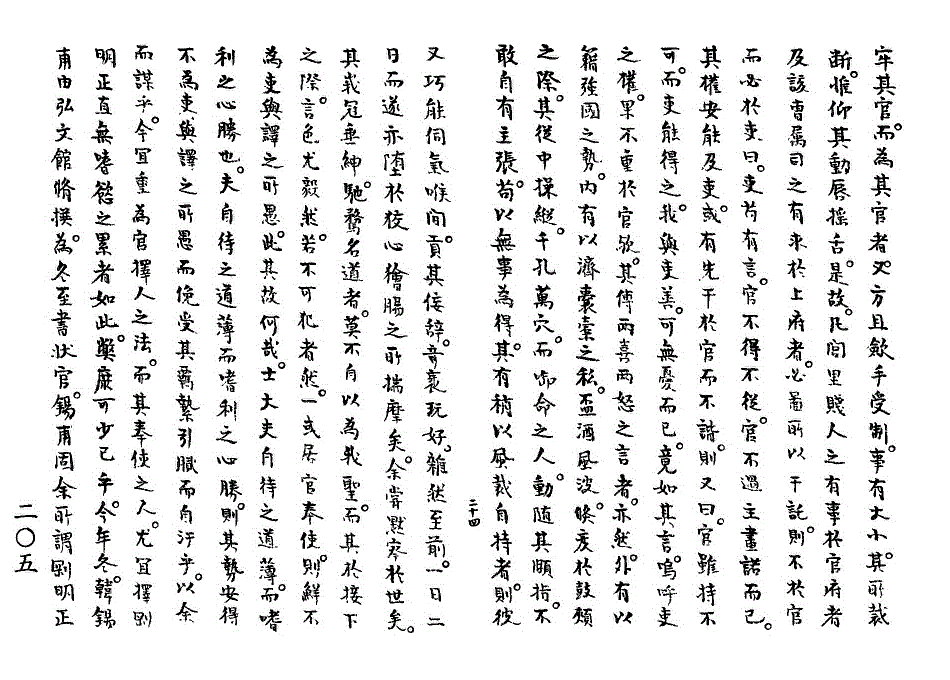 牢其官。而为其官者。又方且敛手受制。事有大小。其所裁断。惟仰其动唇摇舌。是故。凡闾里贱人之有事于官府者及该曹属司之有求于上府者。必啚所以干托。则不于官而必于吏曰。吏苟有言。官不得不从。官不过主画诺而已。其权安能及吏。或有先干于官而不谐。则又曰。官虽持不可。而吏能得之。我与吏善。可无忧而已。竟如其言。呜呼吏之权。果不重于官欤。其传两喜两怒之言者。亦然。外有以籍强国之势。内有以济囊橐之私。杯酒风波。倏变于鼓颊之际。其从中操纵。千孔万穴。而衔命之人。动随其颐指。不敢自有主张。苟以无事为得。其有稍以风裁自持者。则彼又巧能伺气喉间。贡其佞辞。奇邪玩好。杂然至前。一日二日而遂亦堕于狡心狯肠之所揣摩矣。余尝默察于世矣。其峨冠垂绅。驰骛名道者。莫不自以为我圣。而其于接下之际。言色尤毅然。若不可犯者然。一或居官奉使。则鲜不为吏与译之所愚。此其故何哉。士大夫自待之道薄。而嗜利之心胜也。夫自待之道薄而嗜利之心胜。则其势安得不为吏与译之所愚而俛受其羁絷引腻而自污乎。以余而谋乎。今宜重为官择人之法。而其奉使之人。尤宜择刚明正直无嗜欲之累者如此。弊庶可少已乎。今年冬。韩锡甫由弘文馆脩撰。为冬至书状官。锡甫固余所谓刚明正
牢其官。而为其官者。又方且敛手受制。事有大小。其所裁断。惟仰其动唇摇舌。是故。凡闾里贱人之有事于官府者及该曹属司之有求于上府者。必啚所以干托。则不于官而必于吏曰。吏苟有言。官不得不从。官不过主画诺而已。其权安能及吏。或有先干于官而不谐。则又曰。官虽持不可。而吏能得之。我与吏善。可无忧而已。竟如其言。呜呼吏之权。果不重于官欤。其传两喜两怒之言者。亦然。外有以籍强国之势。内有以济囊橐之私。杯酒风波。倏变于鼓颊之际。其从中操纵。千孔万穴。而衔命之人。动随其颐指。不敢自有主张。苟以无事为得。其有稍以风裁自持者。则彼又巧能伺气喉间。贡其佞辞。奇邪玩好。杂然至前。一日二日而遂亦堕于狡心狯肠之所揣摩矣。余尝默察于世矣。其峨冠垂绅。驰骛名道者。莫不自以为我圣。而其于接下之际。言色尤毅然。若不可犯者然。一或居官奉使。则鲜不为吏与译之所愚。此其故何哉。士大夫自待之道薄。而嗜利之心胜也。夫自待之道薄而嗜利之心胜。则其势安得不为吏与译之所愚而俛受其羁絷引腻而自污乎。以余而谋乎。今宜重为官择人之法。而其奉使之人。尤宜择刚明正直无嗜欲之累者如此。弊庶可少已乎。今年冬。韩锡甫由弘文馆脩撰。为冬至书状官。锡甫固余所谓刚明正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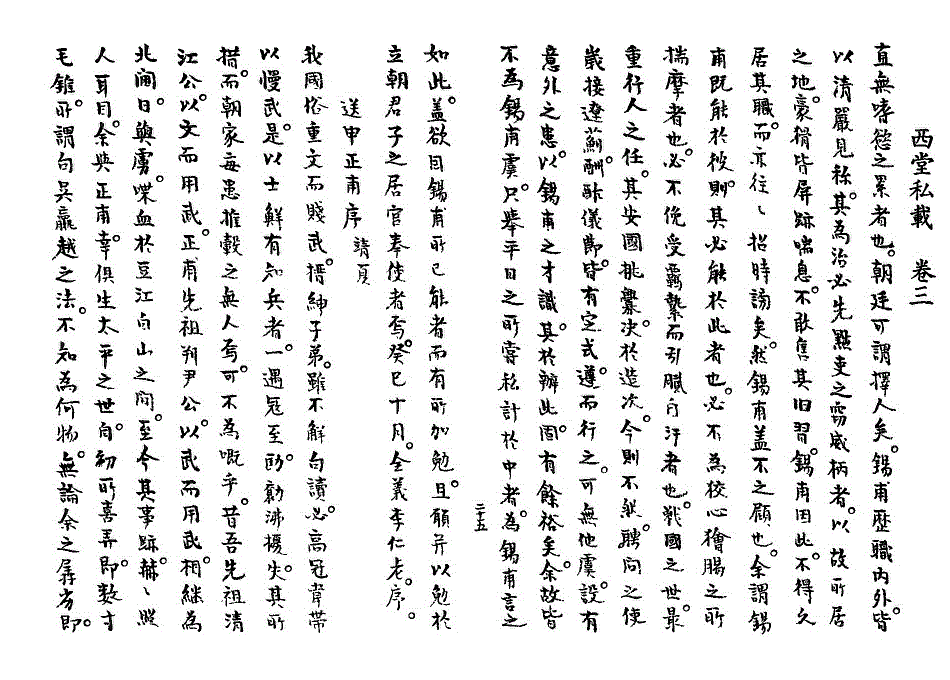 直无嗜欲之累者也。朝廷可谓择人矣。锡甫历职内外。皆以清严见称。其为治必先黜吏之窃威柄者。以故所居之地。豪猾皆屏迹喘息。不敢售其旧习。锡甫因此。不得久居其职。而亦往往招时谤矣。然锡甫盖不之顾也。余谓锡甫既能于彼。则其必能于此者也。必不为狡心狯肠之所揣摩者也。必不俛受羁絷而引腻自污者也。战国之世。最重行人之任。其安国挑衅。决于造次。今则不然。聘问之使岁接辽蓟。酬酢仪节。皆有定式。遵而行之。可无他虞。设有意外之患。以锡甫之才识。其于办此。固有馀裕矣。余故皆不为锡甫虞。只举平日之所尝私计于中者。为锡甫言之如此。盖欲因锡甫所已能者而有所加勉。且愿并以勉于立朝君子之居官奉使者焉。癸巳十月。全义李仁老。序。
直无嗜欲之累者也。朝廷可谓择人矣。锡甫历职内外。皆以清严见称。其为治必先黜吏之窃威柄者。以故所居之地。豪猾皆屏迹喘息。不敢售其旧习。锡甫因此。不得久居其职。而亦往往招时谤矣。然锡甫盖不之顾也。余谓锡甫既能于彼。则其必能于此者也。必不为狡心狯肠之所揣摩者也。必不俛受羁絷而引腻自污者也。战国之世。最重行人之任。其安国挑衅。决于造次。今则不然。聘问之使岁接辽蓟。酬酢仪节。皆有定式。遵而行之。可无他虞。设有意外之患。以锡甫之才识。其于办此。固有馀裕矣。余故皆不为锡甫虞。只举平日之所尝私计于中者。为锡甫言之如此。盖欲因锡甫所已能者而有所加勉。且愿并以勉于立朝君子之居官奉使者焉。癸巳十月。全义李仁老。序。送申正甫序(靖夏)
我国俗重文而贱武。搢绅子弟。虽不解句读。必高冠韦带以慢武。是以士鲜有知兵者。一遇寇至。劻勷沸扰。失其所措。而朝家每患推毂之无人焉。可不为嘅乎。昔吾先祖清江公。以文而用武。正甫先祖判尹公。以武而用武。相继为北阃。日与虏。喋血于豆江白山之间。至今其事迹。赫赫照人耳目。余与正甫。幸俱生太平之世。自幼所喜弄。即数寸毛锥。所谓句吴嬴越之法。不知为何物。无论余之孱劣。即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6L 页
 正甫之英特。其不能继先烈均也。今正甫以兵马评事。北出咸关。将凭览塞上山川。抚二公之遗迹。其必有俯仰今昔之感矣。评事之职。所以赞画戎政。正甫因是行。苟能嘿察北虏风习。揣摩制胜之略。以需他日之用。则是真以文用武。而世之称书生知兵。必将自正甫而始。顾不伟欤。战国时。孙武有知彼知己之论。而汉晁错。亦言中国与凶奴有长有短。夫不料彼己而战。以己之短。攻彼之长。百败而未有一胜者。能料彼己而战。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胜而未有一败者。用兵虽变化多端。而其大要则未有能出此者也。正甫宜嘿察于是。而加以揣摩之密。则其将有得于制胜之方。余敢以余之所不能继先烈者。望于正甫焉。吴君泰兴。北产也。方宰利城。尝为余言曾行过豆江。见越边有三胡腰弓矢骑而驰者。虎起丛薄。迭出而射。其一胡马失前足而倒。虎便跳踉大㘚。血肉狼藉。二胡怒见于色。并驰交射。卒殪其虎。用死胡马。载其尸。并死虎向北而去。其天性悍鸷。不畏死如此。而其马亦甚驯。磬控缓急。唯人意是随。所以所向无敌。我国人心狡诈。避死趍生。即其长技。而马亦与人异意。善惊而𢤱悷。有小兔起于草间。便横逸不可制。以故平原浅草相望之地。我与彼相当。则有类驱羊抵虎。非可冀其一胜者。而我国地多险阸。苟能处处
正甫之英特。其不能继先烈均也。今正甫以兵马评事。北出咸关。将凭览塞上山川。抚二公之遗迹。其必有俯仰今昔之感矣。评事之职。所以赞画戎政。正甫因是行。苟能嘿察北虏风习。揣摩制胜之略。以需他日之用。则是真以文用武。而世之称书生知兵。必将自正甫而始。顾不伟欤。战国时。孙武有知彼知己之论。而汉晁错。亦言中国与凶奴有长有短。夫不料彼己而战。以己之短。攻彼之长。百败而未有一胜者。能料彼己而战。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胜而未有一败者。用兵虽变化多端。而其大要则未有能出此者也。正甫宜嘿察于是。而加以揣摩之密。则其将有得于制胜之方。余敢以余之所不能继先烈者。望于正甫焉。吴君泰兴。北产也。方宰利城。尝为余言曾行过豆江。见越边有三胡腰弓矢骑而驰者。虎起丛薄。迭出而射。其一胡马失前足而倒。虎便跳踉大㘚。血肉狼藉。二胡怒见于色。并驰交射。卒殪其虎。用死胡马。载其尸。并死虎向北而去。其天性悍鸷。不畏死如此。而其马亦甚驯。磬控缓急。唯人意是随。所以所向无敌。我国人心狡诈。避死趍生。即其长技。而马亦与人异意。善惊而𢤱悷。有小兔起于草间。便横逸不可制。以故平原浅草相望之地。我与彼相当。则有类驱羊抵虎。非可冀其一胜者。而我国地多险阸。苟能处处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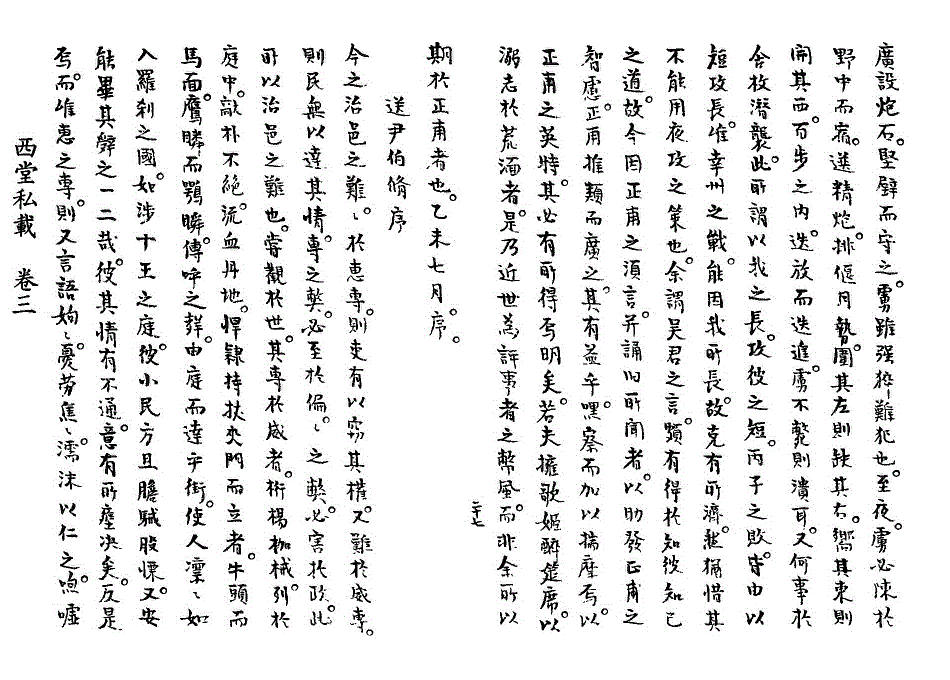 广设炮石。坚壁而守之。虏虽强猝难犯也。至夜。虏必陈于野中而宿。选精炮。排偃月势。围其左则缺其右。向其东则开其西。百步之内。迭放而迭进。虏不毙则溃耳。又何事于含枚潜袭。此所谓以我之长。攻彼之短。丙子之败。皆由以短攻长。唯幸州之战。能因我所长。故克有所济。然犹惜其不能用夜攻之策也。余谓吴君之言。颇有得于知彼知己之道。故今因正甫之须言。并诵旧所闻者。以助发正甫之智虑。正甫推类而广之。其有益乎。嘿察而加以揣摩焉。以正甫之英特。其必有所得焉明矣。若夫拥歌姬醉筵席。以溺志于荒湎者。是乃近世为评事者之币风。而非余所以期于正甫者也。乙未七月。序。
广设炮石。坚壁而守之。虏虽强猝难犯也。至夜。虏必陈于野中而宿。选精炮。排偃月势。围其左则缺其右。向其东则开其西。百步之内。迭放而迭进。虏不毙则溃耳。又何事于含枚潜袭。此所谓以我之长。攻彼之短。丙子之败。皆由以短攻长。唯幸州之战。能因我所长。故克有所济。然犹惜其不能用夜攻之策也。余谓吴君之言。颇有得于知彼知己之道。故今因正甫之须言。并诵旧所闻者。以助发正甫之智虑。正甫推类而广之。其有益乎。嘿察而加以揣摩焉。以正甫之英特。其必有所得焉明矣。若夫拥歌姬醉筵席。以溺志于荒湎者。是乃近世为评事者之币风。而非余所以期于正甫者也。乙未七月。序。送尹伯脩序
今之治邑之难。难于惠专。则吏有以窃其权。又难于威专。则民无以达其情。专之弊。必至于偏。偏之弊。必害于政。此所以治邑之难也。尝观于世。其专于威者。桁杨枷械。列于庭中。敲朴不绝。流血丹地。悍隶持杖夹门而立者。牛头而马面。鹰瞵而鹗瞬。传呼之声。由庭而达乎街。使人凛凛如入罗刹之国。如涉十王之庭。彼小民方且胆駴股慄。又安能毕其辞之一二哉。彼其情有不通。意有所壅决矣。反是焉。而唯惠之专。则又言语姁姁。忧劳焦焦。濡沫以仁之。喣嘘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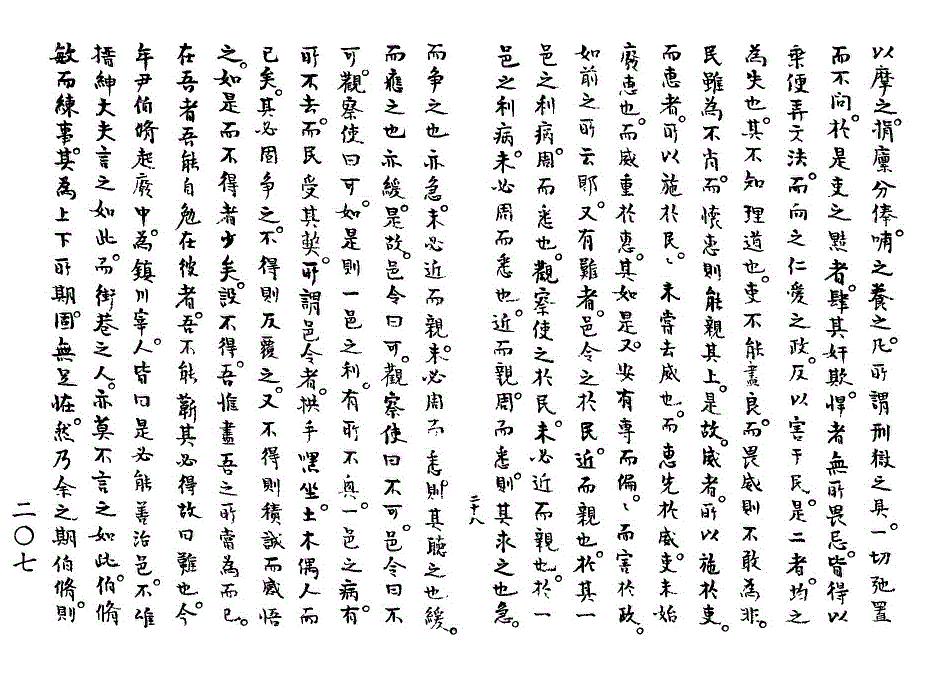 以摩之。捐廪分俸。哺之养之。凡所谓刑狱之具。一切弛置而不问。于是吏之黠者。肆其奸欺。悍者无所畏忌。皆得以乘便弄文法。而向之仁爱之政。反以害于民。是二者。均之为失也。其不知理道也。吏不能尽良。而畏威则不敢为非。民虽为不肖。而怀惠则能亲其上。是故。威者。所以施于吏。而惠者。所以施于民。民未尝去威也。而惠先于威。吏未始废惠也。而威重于惠。其如是。又安有专而偏。偏而害于政。如前之所云耶。又有难者。邑令之于民。近而亲也。于其一邑之利病。周而悉也。观察使之于民。未必近而亲也。于一邑之利病。未必周而悉也。近而亲。周而悉。则其求之也急。而争之也亦急。未必近而亲。未必周而悉。则其听之也缓。而应之也亦缓。是故。邑令曰可。观察使曰不可。邑令曰不可。观察使曰可。如是则一邑之利。有所不兴。一邑之病。有所不去。而民受其弊。所谓邑令者。拱手嘿坐。土木偶人而已矣。其必固争之。不得则反覆之。又不得则积诚而感悟之。如是而不得者少矣。设不得。吾惟尽吾之所当为而已。在吾者吾能自勉。在彼者吾不能蕲其必得。故曰难也。今年尹伯脩起废中。为镇川宰。人皆曰是必能善治邑。不唯搢绅大夫言之如此。而街巷之人。亦莫不言之如此。伯脩敏而练事。其为上下所期。固无足怪。然乃余之期伯脩。则
以摩之。捐廪分俸。哺之养之。凡所谓刑狱之具。一切弛置而不问。于是吏之黠者。肆其奸欺。悍者无所畏忌。皆得以乘便弄文法。而向之仁爱之政。反以害于民。是二者。均之为失也。其不知理道也。吏不能尽良。而畏威则不敢为非。民虽为不肖。而怀惠则能亲其上。是故。威者。所以施于吏。而惠者。所以施于民。民未尝去威也。而惠先于威。吏未始废惠也。而威重于惠。其如是。又安有专而偏。偏而害于政。如前之所云耶。又有难者。邑令之于民。近而亲也。于其一邑之利病。周而悉也。观察使之于民。未必近而亲也。于一邑之利病。未必周而悉也。近而亲。周而悉。则其求之也急。而争之也亦急。未必近而亲。未必周而悉。则其听之也缓。而应之也亦缓。是故。邑令曰可。观察使曰不可。邑令曰不可。观察使曰可。如是则一邑之利。有所不兴。一邑之病。有所不去。而民受其弊。所谓邑令者。拱手嘿坐。土木偶人而已矣。其必固争之。不得则反覆之。又不得则积诚而感悟之。如是而不得者少矣。设不得。吾惟尽吾之所当为而已。在吾者吾能自勉。在彼者吾不能蕲其必得。故曰难也。今年尹伯脩起废中。为镇川宰。人皆曰是必能善治邑。不唯搢绅大夫言之如此。而街巷之人。亦莫不言之如此。伯脩敏而练事。其为上下所期。固无足怪。然乃余之期伯脩。则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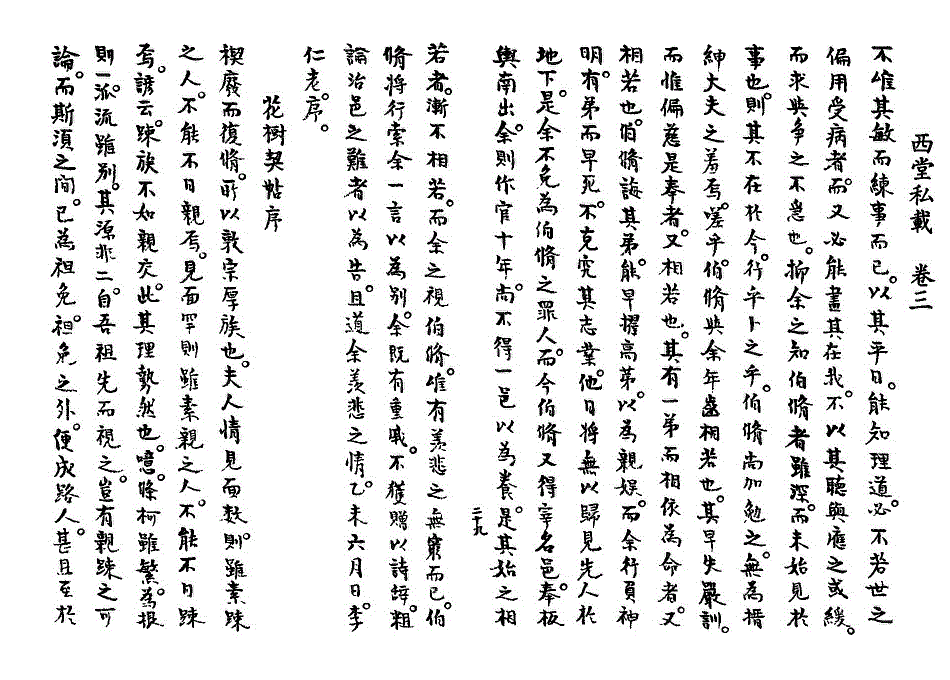 不唯其敏而练事而已。以其平日。能知理道。必不若世之偏用受病者。而又必能尽其在我。不以其听与应之或缓。而求与争之不急也。抑余之知伯脩者虽深。而未始见于事也。则其不在于今。行乎卜之乎。伯脩尚加勉之。无为搢绅大夫之羞焉。嗟乎。伯脩与余年齿相若也。其早失严训。而惟偏慈是奉者。又相若也。其有一弟而相依为命者。又相若也。伯脩诲其弟。能早擢高第。以为亲娱。而余行负神明。有弟而早死。不克究其志业。他日将无以归见先人于地下。是余不免为伯脩之罪人。而今伯脩又得宰名邑。奉板舆南出。余则作官十年。尚不得一邑以为养。是其始之相若者。渐不相若。而余之视伯脩。唯有羡悲之无穷而已。伯脩将行索余一言以为别。余既有重戚。不获赠以诗辞。粗论治邑之难者以为告。且道余羡悲之情。乙未六月日。李仁老。序。
不唯其敏而练事而已。以其平日。能知理道。必不若世之偏用受病者。而又必能尽其在我。不以其听与应之或缓。而求与争之不急也。抑余之知伯脩者虽深。而未始见于事也。则其不在于今。行乎卜之乎。伯脩尚加勉之。无为搢绅大夫之羞焉。嗟乎。伯脩与余年齿相若也。其早失严训。而惟偏慈是奉者。又相若也。其有一弟而相依为命者。又相若也。伯脩诲其弟。能早擢高第。以为亲娱。而余行负神明。有弟而早死。不克究其志业。他日将无以归见先人于地下。是余不免为伯脩之罪人。而今伯脩又得宰名邑。奉板舆南出。余则作官十年。尚不得一邑以为养。是其始之相若者。渐不相若。而余之视伯脩。唯有羡悲之无穷而已。伯脩将行索余一言以为别。余既有重戚。不获赠以诗辞。粗论治邑之难者以为告。且道余羡悲之情。乙未六月日。李仁老。序。花树契帖序
稧废而复脩。所以敦宗厚族也。夫人情见面数。则虽素疏之人。不能不日亲焉。见面罕则虽素亲之人。不能不日疏焉。谚云。疏族不如亲交。此其理势然也。噫。条柯虽繁。为根则一。派流虽别。其源非二。自吾祖先而视之。岂有亲疏之可论。而斯须之间。已为袒免。袒免之外。便成路人。甚且至于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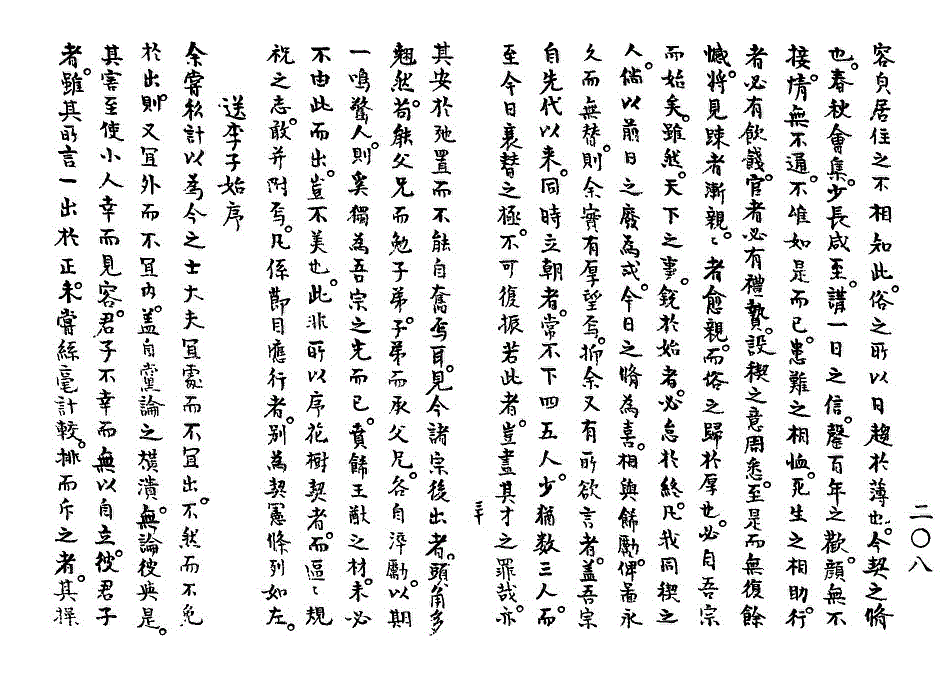 容貌居住之不相知此。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今契之脩也。春秋会集。少长咸至。讲一日之信。罄百年之欢。颜无不接。情无不通。不唯如是而已。患难之相恤。死生之相助。行者必有饮饯。官者必有礼贽。设稧之意周悉。至是而无复馀憾。将见疏者渐亲。亲者愈亲。而俗之归于厚也。必自吾宗而始矣。虽然。天下之事。锐于始者。必怠于终。凡我同稧之人。倘以前日之废为戒。今日之脩为喜。相与饰励。俾啚永久而无替。则余实有厚望焉。抑余又有所欲言者。盖吾宗自先代以来。同时立朝者。常不下四五人。少犹数三人。而至今日衰替之极。不可复振若此者。岂尽其才之罪哉。亦其安于弛置而不能自奋焉耳。见今诸宗后出者。头角多翘然。苟能父兄而勉子弟。子弟而承父兄。各自淬励。以期一鸣惊人。则奚独为吾宗之光而已。贲饰王猷之材。未必不由此而出。岂不美也。此非所以序花树契者。而区区规祝之志。敢并附焉。凡系节目应行者。别为契宪条列如左。
容貌居住之不相知此。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今契之脩也。春秋会集。少长咸至。讲一日之信。罄百年之欢。颜无不接。情无不通。不唯如是而已。患难之相恤。死生之相助。行者必有饮饯。官者必有礼贽。设稧之意周悉。至是而无复馀憾。将见疏者渐亲。亲者愈亲。而俗之归于厚也。必自吾宗而始矣。虽然。天下之事。锐于始者。必怠于终。凡我同稧之人。倘以前日之废为戒。今日之脩为喜。相与饰励。俾啚永久而无替。则余实有厚望焉。抑余又有所欲言者。盖吾宗自先代以来。同时立朝者。常不下四五人。少犹数三人。而至今日衰替之极。不可复振若此者。岂尽其才之罪哉。亦其安于弛置而不能自奋焉耳。见今诸宗后出者。头角多翘然。苟能父兄而勉子弟。子弟而承父兄。各自淬励。以期一鸣惊人。则奚独为吾宗之光而已。贲饰王猷之材。未必不由此而出。岂不美也。此非所以序花树契者。而区区规祝之志。敢并附焉。凡系节目应行者。别为契宪条列如左。送李子始序
余尝私计以为今之士大夫宜处而不宜出。不然而不免于出。则又宜外而不宜内。盖自党论之横溃。无论彼与是。其害至使小人幸而见容。君子不幸而无以自立。彼君子者。虽其所言一出于正。未尝丝毫计较。排而斥之者。其操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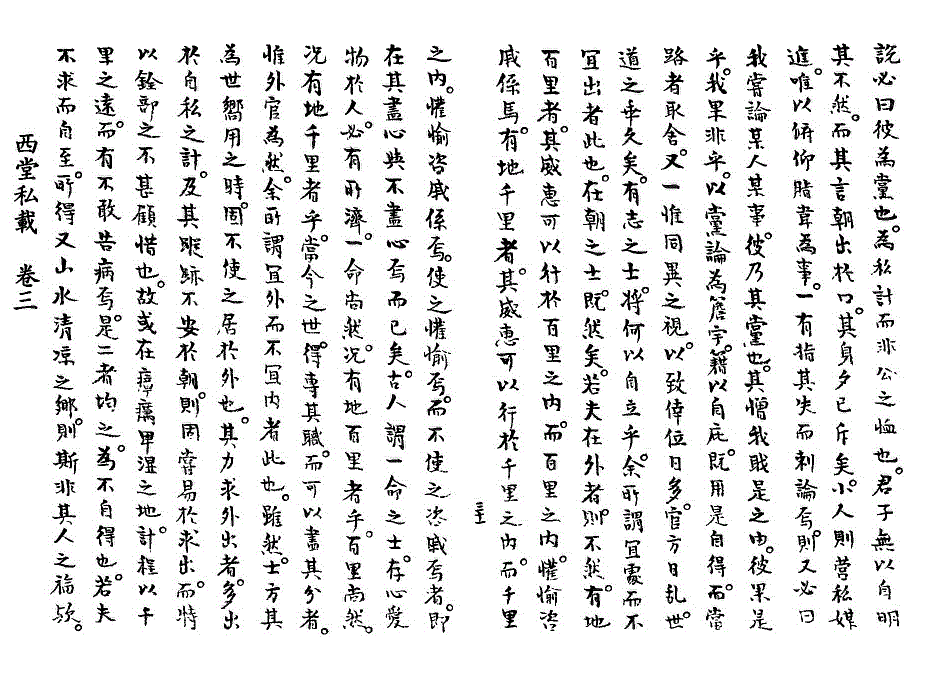 说必曰彼为党也。为私计而非公之恤也。君子无以自明其不然。而其言朝出于口。其身夕已斥矣。小人则营私媒进。唯以俯仰脂韦为事。一有指其失而刺论焉。则又必曰我尝论某人某事。彼乃其党也。其憎我职是之由。彼果是乎。我果非乎。以党论为檐宇。籍以自庇。既用是自得。而当路者取舍。又一惟同异之视。以致倖位日多。官方日乱。世道之乖久矣。有志之士。将何以自立乎。余所谓宜处而不宜出者此也。在朝之士。既然矣。若夫在外者。则不然。有地百里者。其威惠可以行于百里之内。而百里之内。欢愉咨戚系焉。有地千里者。其威惠可以行于千里之内。而千里之内。欢愉咨戚系焉。使之欢愉焉。而不使之咨戚焉者。即在其尽心与不尽心焉而已矣。古人谓一命之士。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一命尚然。况有地百里者乎。百里尚然。况有地千里者乎。当今之世。得专其职。而可以尽其分者。惟外官为然。余所谓宜外而不宜内者此也。虽然。士方其为世向用之时。固不使之居于外也。其力求外出者。多出于自私之计。及其踪迹不安于朝。则固尝易于求出。而特以铨部之不甚顾惜也。故或在瘴疠卑湿之地。计程以千里之远。而有不敢告病焉。是二者均之。为不自得也。若夫不求而自至。所得又山水清凉之乡。则斯非其人之福欤。
说必曰彼为党也。为私计而非公之恤也。君子无以自明其不然。而其言朝出于口。其身夕已斥矣。小人则营私媒进。唯以俯仰脂韦为事。一有指其失而刺论焉。则又必曰我尝论某人某事。彼乃其党也。其憎我职是之由。彼果是乎。我果非乎。以党论为檐宇。籍以自庇。既用是自得。而当路者取舍。又一惟同异之视。以致倖位日多。官方日乱。世道之乖久矣。有志之士。将何以自立乎。余所谓宜处而不宜出者此也。在朝之士。既然矣。若夫在外者。则不然。有地百里者。其威惠可以行于百里之内。而百里之内。欢愉咨戚系焉。有地千里者。其威惠可以行于千里之内。而千里之内。欢愉咨戚系焉。使之欢愉焉。而不使之咨戚焉者。即在其尽心与不尽心焉而已矣。古人谓一命之士。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一命尚然。况有地百里者乎。百里尚然。况有地千里者乎。当今之世。得专其职。而可以尽其分者。惟外官为然。余所谓宜外而不宜内者此也。虽然。士方其为世向用之时。固不使之居于外也。其力求外出者。多出于自私之计。及其踪迹不安于朝。则固尝易于求出。而特以铨部之不甚顾惜也。故或在瘴疠卑湿之地。计程以千里之远。而有不敢告病焉。是二者均之。为不自得也。若夫不求而自至。所得又山水清凉之乡。则斯非其人之福欤。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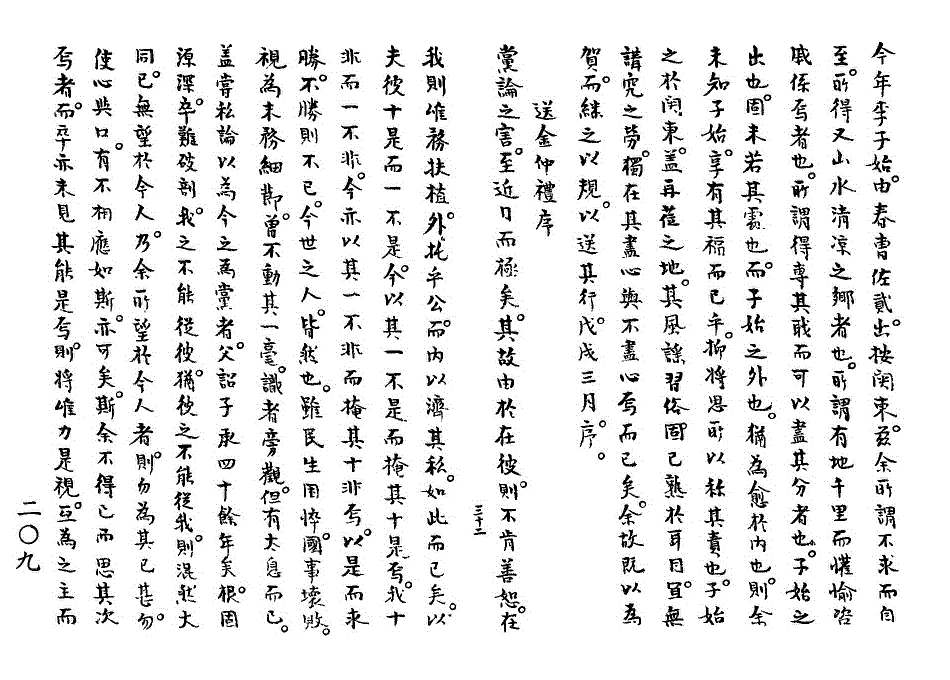 今年李子始。由春曹佐贰。出按关东。玆余所谓不求而自至。所得又山水清凉之乡者也。所谓有地千里而欢愉咨戚系焉者也。所谓得专其职而可以尽其分者也。子始之出也。固未若其处也。而子始之外也。犹为愈于内也。则余未知子始。享有其福而已乎。抑将思所以称其责也。子始之于关东。盖再莅之地。其风谣习俗。固已熟于耳目。宜无讲究之劳。独在其尽心与不尽心焉而已矣。余故既以为贺。而继之以规。以送其行。戊戌三月。序。
今年李子始。由春曹佐贰。出按关东。玆余所谓不求而自至。所得又山水清凉之乡者也。所谓有地千里而欢愉咨戚系焉者也。所谓得专其职而可以尽其分者也。子始之出也。固未若其处也。而子始之外也。犹为愈于内也。则余未知子始。享有其福而已乎。抑将思所以称其责也。子始之于关东。盖再莅之地。其风谣习俗。固已熟于耳目。宜无讲究之劳。独在其尽心与不尽心焉而已矣。余故既以为贺。而继之以规。以送其行。戊戌三月。序。送金仲礼序
党论之害。至近日而极矣。其故由于在彼。则不肯善恕。在我则唯务扶植。外以托乎公。而内以济其私。如此而已矣。夫彼十是而一不是。今以其一不是而掩其十是焉。我十非而一不非。今亦以其一不非而掩其十非焉。以是而求胜。不胜则不已。今世之人。皆然也。虽民生困悴。国事坏败。视为末务细节。曾不动其一毫。识者旁观。但有太息而已。盖尝私论以为今之为党者。父诏子承四十馀年矣。根固源深。卒难破剖。我之不能从彼。犹彼之不能从我。则混然大同。已无望于今人。乃余所望于今人者。则勿为其已甚。勿使心与口。有不相应如斯。亦可矣。斯余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者。而卒亦未见其能是焉。则将唯力是视。互为之主而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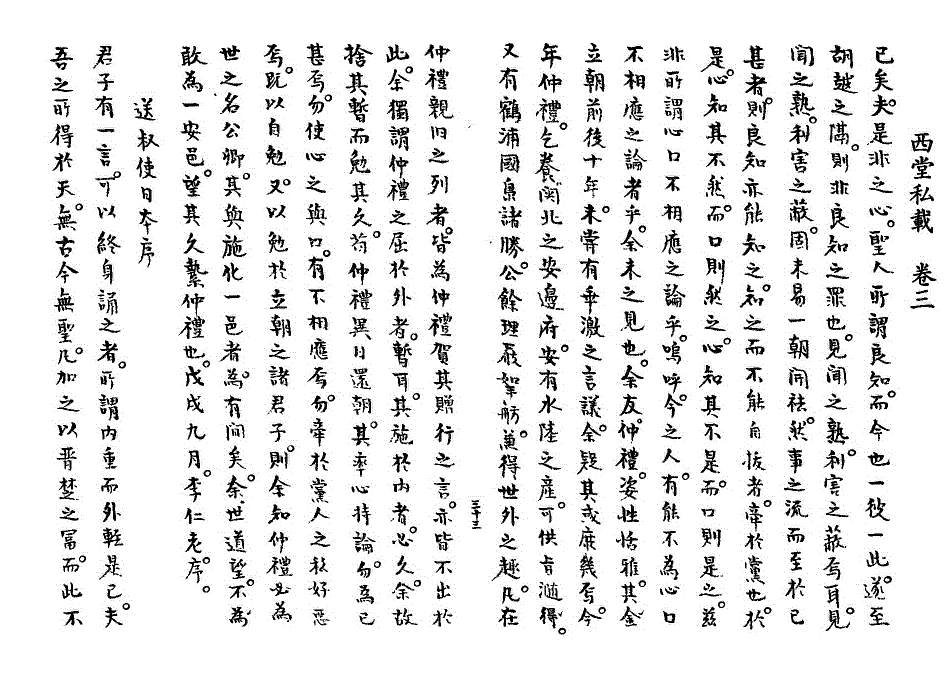 已矣。夫是非之心。圣人所谓良知。而今也一彼一此。遂至胡越之隔。则非良知之罪也。见闻之熟。利害之蔽焉耳。见闻之熟。利害之蔽。固未易一朝开祛。然事之流而至于已甚者。则良知亦能知之。知之而不能自拔者。牵于党也。于是。心知其不然。而口则然之。心知其不是。而口则是之。玆非所谓心口不相应之论乎。呜呼。今之人。有能不为心口不相应之论者乎。余未之见也。余友金仲礼。姿性恬雅。其立朝前后十年。未尝有乖激之言议。余疑其或庶几焉。今年仲礼。乞养得关北之安边府。安有水陆之产。可供旨瀡。又有鹤浦国枭诸胜。公馀理屐挐舫。兼得世外之趣。凡在仲礼亲旧之列者。皆为仲礼贺其赠行之言。亦皆不出于此。余独谓仲礼之屈于外者。暂耳。其施于内者。必久。余故舍其暂而勉其久。苟仲礼异日还朝。其率心持论。勿为已甚焉。勿使心之与口。有不相应焉。勿牵于党人之私好恶焉。既以自勉。又以勉于立朝之诸君子。则余知仲礼必为世之名公卿。其与施化一邑者。为有间矣。余为世道望。不敢为一安邑。望其久絷仲礼也。戊戌九月。李仁老。序。
已矣。夫是非之心。圣人所谓良知。而今也一彼一此。遂至胡越之隔。则非良知之罪也。见闻之熟。利害之蔽焉耳。见闻之熟。利害之蔽。固未易一朝开祛。然事之流而至于已甚者。则良知亦能知之。知之而不能自拔者。牵于党也。于是。心知其不然。而口则然之。心知其不是。而口则是之。玆非所谓心口不相应之论乎。呜呼。今之人。有能不为心口不相应之论者乎。余未之见也。余友金仲礼。姿性恬雅。其立朝前后十年。未尝有乖激之言议。余疑其或庶几焉。今年仲礼。乞养得关北之安边府。安有水陆之产。可供旨瀡。又有鹤浦国枭诸胜。公馀理屐挐舫。兼得世外之趣。凡在仲礼亲旧之列者。皆为仲礼贺其赠行之言。亦皆不出于此。余独谓仲礼之屈于外者。暂耳。其施于内者。必久。余故舍其暂而勉其久。苟仲礼异日还朝。其率心持论。勿为已甚焉。勿使心之与口。有不相应焉。勿牵于党人之私好恶焉。既以自勉。又以勉于立朝之诸君子。则余知仲礼必为世之名公卿。其与施化一邑者。为有间矣。余为世道望。不敢为一安邑。望其久絷仲礼也。戊戌九月。李仁老。序。送叔使日本序
君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诵之者。所谓内重而外轻是已。夫吾之所得于天。无古今无圣。凡加之以晋楚之富。而此不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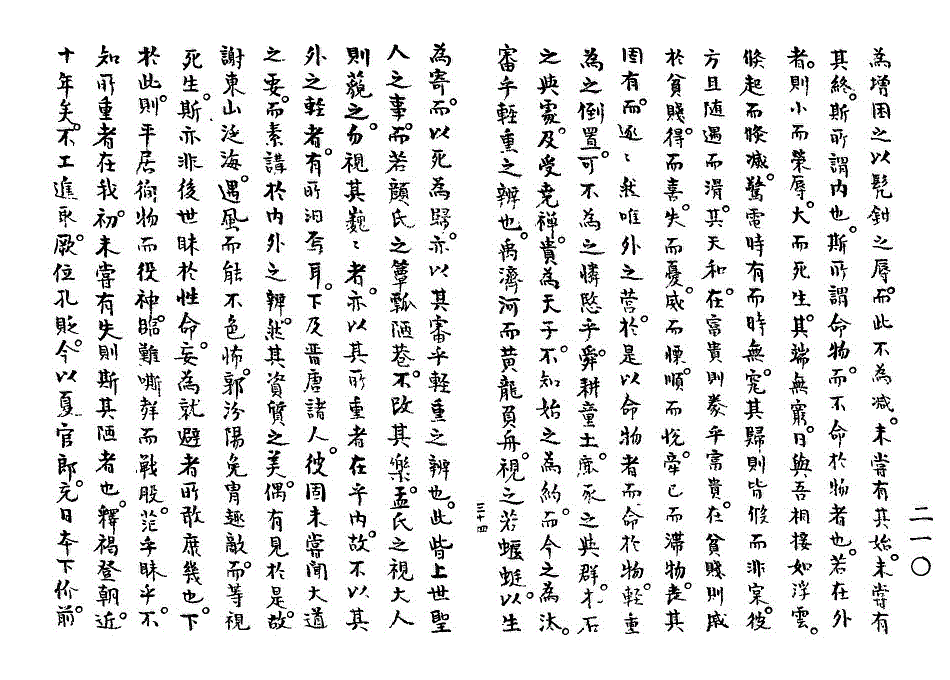 为增困之以髡钳之辱。而此不为减。未尝有其始。未尝有其终。斯所谓内也。斯所谓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若在外者。则小而荣辱。大而死生。其端无穷。日与吾相接如浮云。倏起而倏灭。惊电时有而时无。究其归则皆假而非实。彼方且随遇而滑。其天和。在富贵则豢乎富贵。在贫贱则戚于贫贱。得而喜。失而忧。威而慄。顺而悦。牵己而滞物。丧其固有。而逐逐然唯外之营。于是以命物者而命于物。轻重为之倒置。可不为之怜悯乎。舜耕童土。鹿豕之与群。木石之与处。及受尧禅。贵为天子。不知始之为约。而今之为汰。审乎轻重之辨也。禹济河而黄龙负舟。视之若蝘蜓。以生为寄。而以死为归。亦以其审乎轻重之辨也。此皆上世圣人之事。而若颜氏之簟瓢陋巷。不改其乐。孟氏之视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者。亦以其所重者在乎内。故不以其外之轻者。有所汩焉耳。下及晋唐诸人。彼固未尝闻大道之要。而素讲于内外之辨。然其资质之美。偶有见于是。故谢东山泛海。遇风而能不色怖。郭汾阳免冑趣敌。而等视死生。斯亦非后世眛于性命。妄为就避者所敢庶几也。下于此。则平居徇物而役神。临难嘶声而战股。茫乎眛乎。不知所重者在我。初未尝有失则斯其陋者也。释褐登朝。近十年矣。不工进取。厥位孔贬。今以夏官郎。充日本下价。前
为增困之以髡钳之辱。而此不为减。未尝有其始。未尝有其终。斯所谓内也。斯所谓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若在外者。则小而荣辱。大而死生。其端无穷。日与吾相接如浮云。倏起而倏灭。惊电时有而时无。究其归则皆假而非实。彼方且随遇而滑。其天和。在富贵则豢乎富贵。在贫贱则戚于贫贱。得而喜。失而忧。威而慄。顺而悦。牵己而滞物。丧其固有。而逐逐然唯外之营。于是以命物者而命于物。轻重为之倒置。可不为之怜悯乎。舜耕童土。鹿豕之与群。木石之与处。及受尧禅。贵为天子。不知始之为约。而今之为汰。审乎轻重之辨也。禹济河而黄龙负舟。视之若蝘蜓。以生为寄。而以死为归。亦以其审乎轻重之辨也。此皆上世圣人之事。而若颜氏之簟瓢陋巷。不改其乐。孟氏之视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者。亦以其所重者在乎内。故不以其外之轻者。有所汩焉耳。下及晋唐诸人。彼固未尝闻大道之要。而素讲于内外之辨。然其资质之美。偶有见于是。故谢东山泛海。遇风而能不色怖。郭汾阳免冑趣敌。而等视死生。斯亦非后世眛于性命。妄为就避者所敢庶几也。下于此。则平居徇物而役神。临难嘶声而战股。茫乎眛乎。不知所重者在我。初未尝有失则斯其陋者也。释褐登朝。近十年矣。不工进取。厥位孔贬。今以夏官郎。充日本下价。前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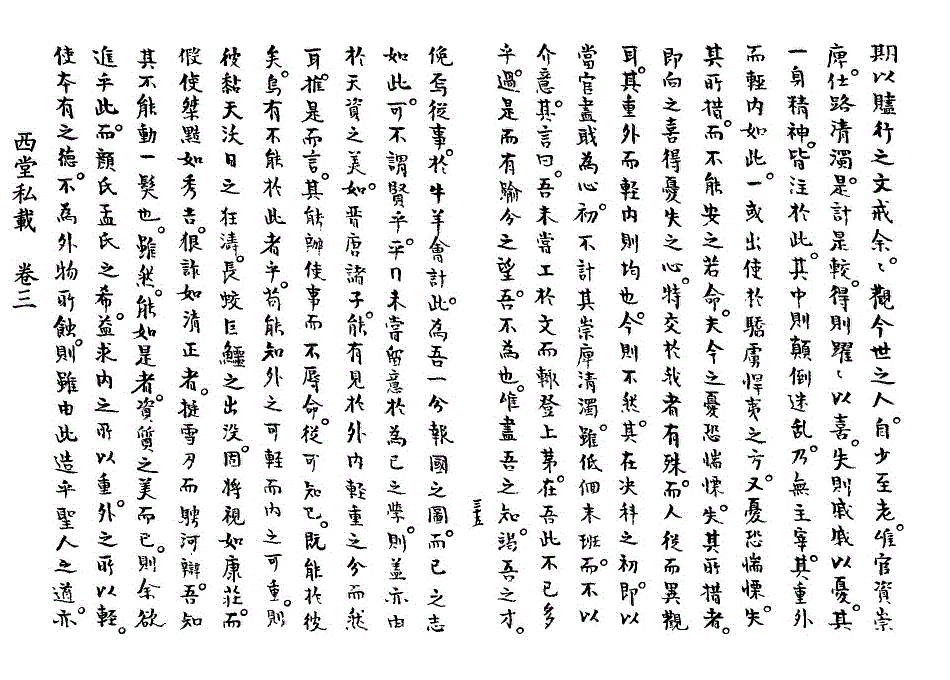 期以赆行之文戒余。余观今世之人。自少至老。唯官资崇庳。仕路清浊。是计是较。得则跃跃以喜。失则戚戚以忧。其一身精神。皆注于此。其中则颠倒迷乱。乃无主宰。其重外而轻内如此。一或出使于骄虏悍夷之方。又忧恐惴慄。失其所措。而不能安之若命。夫今之忧恐惴慄。失其所措者。即向之喜得忧失之心。特交于我者有殊。而人从而异观耳。其重外而轻内则均也。今则不然。其在决科之初。即以当官尽职为心。初不计其崇庳清浊。虽低佪末班。而不以介意。其言曰。吾未尝工于文而辄登上第。在吾此不已多乎。过是而有踰分之望。吾不为也。唯尽吾之知。竭吾之才。俛焉从事。于牛羊会计。此为吾一分报国之图。而己之志如此。可不谓贤乎。平日未尝留意于为己之学。则盖亦由于天资之美。如晋唐诸子。能有见于外内轻重之分而然耳。推是而言。其能办使事而不辱命。从可知已。既能于彼矣。乌有不能于此者乎。苟能知外之可轻而内之可重。则彼黏天沃日之狂涛。长蛟巨鳄之出没。固将视如康庄。而假使桀黠如秀吉。狠诈如清正者。挺雪刃而骋河辩。吾知其不能动一发也。虽然。能如是者。资质之美而已。则余欲进乎此。而颜氏孟氏之希。益求内之所以重。外之所以轻。使本有之德。不为外物所蚀。则虽由此造乎圣人之道。亦
期以赆行之文戒余。余观今世之人。自少至老。唯官资崇庳。仕路清浊。是计是较。得则跃跃以喜。失则戚戚以忧。其一身精神。皆注于此。其中则颠倒迷乱。乃无主宰。其重外而轻内如此。一或出使于骄虏悍夷之方。又忧恐惴慄。失其所措。而不能安之若命。夫今之忧恐惴慄。失其所措者。即向之喜得忧失之心。特交于我者有殊。而人从而异观耳。其重外而轻内则均也。今则不然。其在决科之初。即以当官尽职为心。初不计其崇庳清浊。虽低佪末班。而不以介意。其言曰。吾未尝工于文而辄登上第。在吾此不已多乎。过是而有踰分之望。吾不为也。唯尽吾之知。竭吾之才。俛焉从事。于牛羊会计。此为吾一分报国之图。而己之志如此。可不谓贤乎。平日未尝留意于为己之学。则盖亦由于天资之美。如晋唐诸子。能有见于外内轻重之分而然耳。推是而言。其能办使事而不辱命。从可知已。既能于彼矣。乌有不能于此者乎。苟能知外之可轻而内之可重。则彼黏天沃日之狂涛。长蛟巨鳄之出没。固将视如康庄。而假使桀黠如秀吉。狠诈如清正者。挺雪刃而骋河辩。吾知其不能动一发也。虽然。能如是者。资质之美而已。则余欲进乎此。而颜氏孟氏之希。益求内之所以重。外之所以轻。使本有之德。不为外物所蚀。则虽由此造乎圣人之道。亦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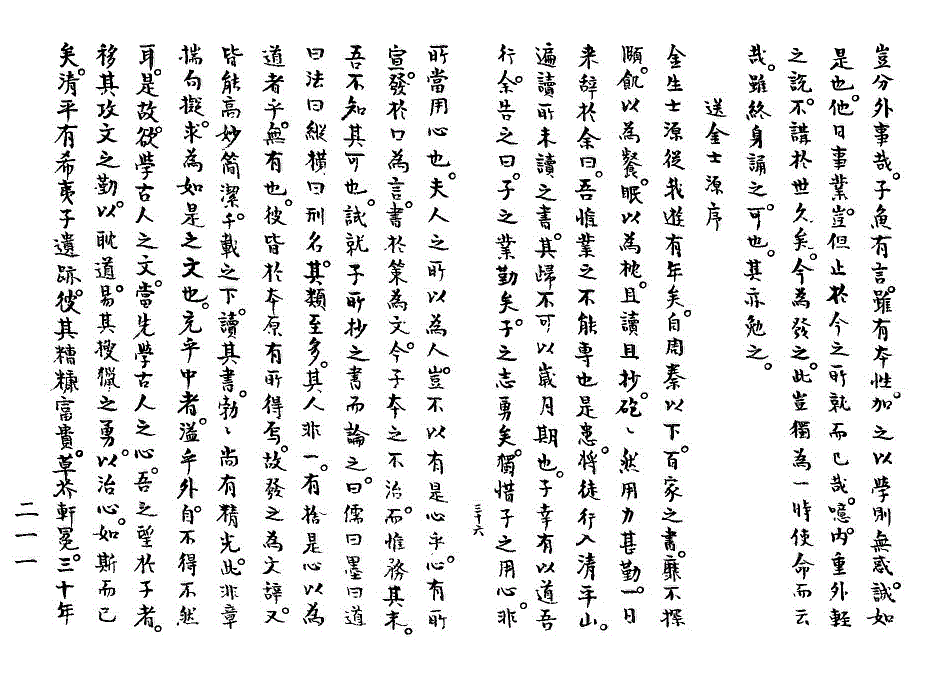 岂分外事哉。子鱼有言。虽有本性。加之以学则无惑。诚如是也。他日事业。岂但止于今之所就而已哉。噫。内重外轻之说。不讲于世久矣。今为发之。此岂独为一时使命而云哉。虽终身诵之。可也。其亦勉之。
岂分外事哉。子鱼有言。虽有本性。加之以学则无惑。诚如是也。他日事业。岂但止于今之所就而已哉。噫。内重外轻之说。不讲于世久矣。今为发之。此岂独为一时使命而云哉。虽终身诵之。可也。其亦勉之。送金士源序
金生士源从我游有年矣。自周秦以下。百家之书。靡不探颐。饥以为餐。眠以为枕。且读且抄。炮炮然用力甚勤。一日来辞于余曰。吾惟业之不能专也是患。将徒行入清平山。遍读所未读之书。其归不可以岁月期也。子幸有以道吾行。余告之曰。子之业勤矣。子之志勇矣。独惜子之用心。非所当用心也。夫人之所以为人。岂不以有是心乎。心有所宣。发于口为言。书于策为文。今子本之不治。而惟务其末。吾不知其可也。试就子所抄之书而论之。曰儒曰墨曰道曰法曰纵横曰刑名。其类至多。其人非一。有舍是心以为道者乎。无有也。彼皆于本原有所得焉。故发之为文辞。又皆能高妙简洁。千载之下。读其书。勃勃尚有精光。此非章揣句拟。求为如是之文也。充乎中者。溢乎外。自不得不然耳。是故。欲学古人之文。当先学古人之心。吾之望于子者。移其攻文之勤。以耽道。易其搜猎之勇。以治心。如斯而已矣。清平有希夷子遗迹。彼其糟糠富贵。草芥轩冕。三十年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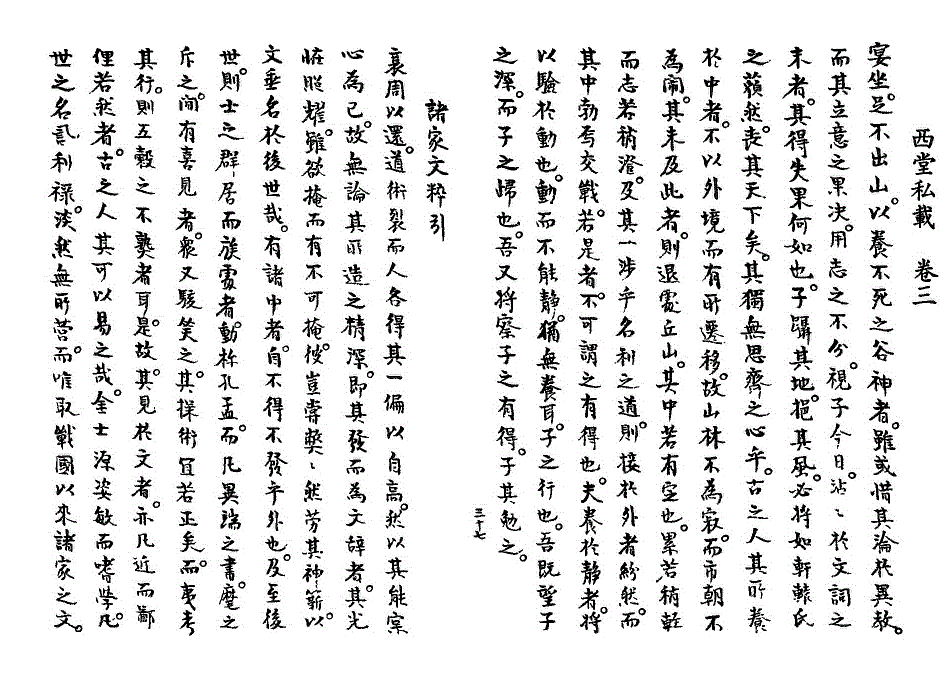 宴坐。足不出山。以养不死之谷神者。虽或惜其沦于异教。而其立意之果决。用志之不分。视子今日。沾沾于文词之末者。其得失果何如也。子蹑其地。挹其风。必将如轩辕氏之藐然。丧其天下矣。其独无思齐之心乎。古之人其所养于中者。不以外境而有所迁移。故山林不为寂。而市朝不为闹。其未及此者。则退处丘山。其中若有定也。累若稍轻而志若稍澄。及其一涉乎名利之道。则接于外者纷然。而其中勃焉交战。若是者。不可谓之有得也。夫养于静者。将以验于动也。动而不能静。犹无养耳。子之行也。吾既望子之深。而子之归也。吾又将察子之有得。子其勉之。
宴坐。足不出山。以养不死之谷神者。虽或惜其沦于异教。而其立意之果决。用志之不分。视子今日。沾沾于文词之末者。其得失果何如也。子蹑其地。挹其风。必将如轩辕氏之藐然。丧其天下矣。其独无思齐之心乎。古之人其所养于中者。不以外境而有所迁移。故山林不为寂。而市朝不为闹。其未及此者。则退处丘山。其中若有定也。累若稍轻而志若稍澄。及其一涉乎名利之道。则接于外者纷然。而其中勃焉交战。若是者。不可谓之有得也。夫养于静者。将以验于动也。动而不能静。犹无养耳。子之行也。吾既望子之深。而子之归也。吾又将察子之有得。子其勉之。诸家文粹引
衰周以还。道术裂而人各得其一偏以自高。然以其能实心为己。故无论其所造之精深。即其发而为文辞者。其光怪照耀。虽欲掩而有不可掩。彼岂尝弊弊然劳其神蕲。以文垂名于后世哉。有诸中者。自不得不发乎外也。及至后世。则士之群居而族处者。动称孔孟。而凡异端之书。麾之斥之。间有喜见者。众又骇笑之。其操术宜若正矣。而夷考其行。则五谷之不熟者耳。是故。其见于文者。亦凡近而鄙俚若然者。古之人其可以易之哉。金士源姿敏而嗜学。凡世之名誉利禄。淡然无所营。而唯取战国以来诸家之文。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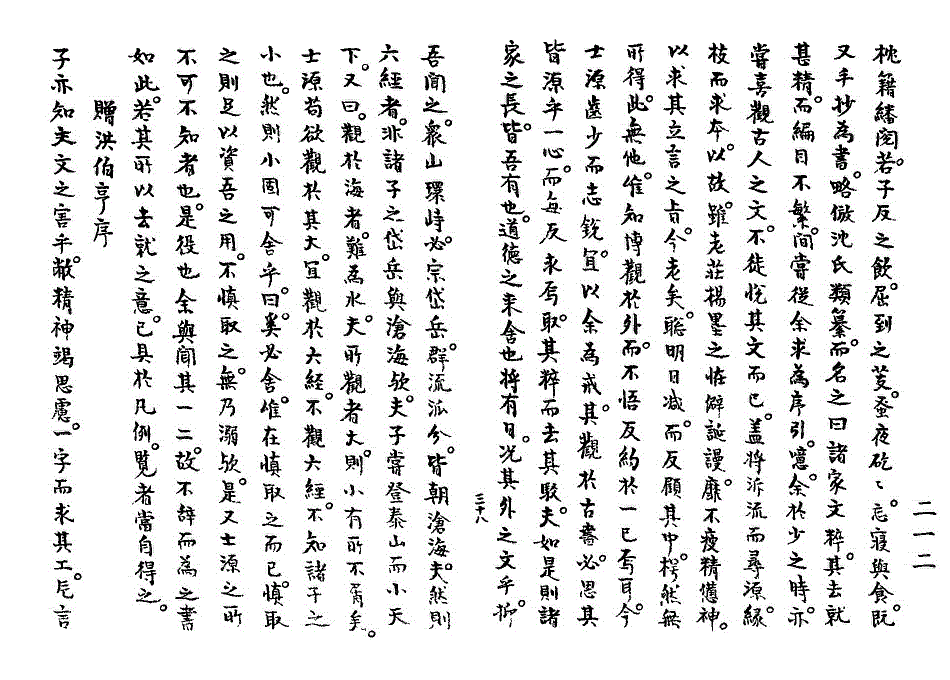 枕籍翻阅。若子反之饮。屈到之芰。蚤夜矻矻。忘寝与食。既又手抄为书。略仿沈氏类纂。而名之曰诸家文粹。其去就甚精。而编目不繁。间尝从余求为序引。噫。余于少之时。亦尝喜观古人之文。不徒悦其文而已。盖将溯流而寻源。缘枝而求本。以故。虽老庄杨墨之怪僻诞谩。靡不疲精惫神。以求其立言之旨。今老矣。聪明日减。而反顾其中。枵然无所得。此无他。唯知博观于外。而不悟反约于一己焉耳。今士源齿少而志锐。宜以余为戒。其观于古书。必思其皆源乎一心。而每反求焉。取其粹而去其驳。夫如是则诸家之长。皆吾有也。道德之来舍也将有日。况其外之文乎。抑吾闻之。众山环峙。必宗岱岳。群流派分。皆朝沧海。夫然则六经者。非诸子之岱岳与沧海欤。夫子尝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观于海者。难为水。夫所观者大。则小有所不屑矣。士源苟欲观于其大。宜观于六经。不观六经。不知诸子之小也。然则小固可舍乎。曰。奚必舍。唯在慎取之而已。慎取之则足以资吾之用。不慎取之。无乃溺欤。是又士源之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役也余与闻其一二。故不辞而为之书如此。若其所以去就之意。已具于凡例。览者当自得之。
枕籍翻阅。若子反之饮。屈到之芰。蚤夜矻矻。忘寝与食。既又手抄为书。略仿沈氏类纂。而名之曰诸家文粹。其去就甚精。而编目不繁。间尝从余求为序引。噫。余于少之时。亦尝喜观古人之文。不徒悦其文而已。盖将溯流而寻源。缘枝而求本。以故。虽老庄杨墨之怪僻诞谩。靡不疲精惫神。以求其立言之旨。今老矣。聪明日减。而反顾其中。枵然无所得。此无他。唯知博观于外。而不悟反约于一己焉耳。今士源齿少而志锐。宜以余为戒。其观于古书。必思其皆源乎一心。而每反求焉。取其粹而去其驳。夫如是则诸家之长。皆吾有也。道德之来舍也将有日。况其外之文乎。抑吾闻之。众山环峙。必宗岱岳。群流派分。皆朝沧海。夫然则六经者。非诸子之岱岳与沧海欤。夫子尝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观于海者。难为水。夫所观者大。则小有所不屑矣。士源苟欲观于其大。宜观于六经。不观六经。不知诸子之小也。然则小固可舍乎。曰。奚必舍。唯在慎取之而已。慎取之则足以资吾之用。不慎取之。无乃溺欤。是又士源之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役也余与闻其一二。故不辞而为之书如此。若其所以去就之意。已具于凡例。览者当自得之。赠洪伯亨序
子亦知夫文之害乎。敝精神竭思虑。一字而求其工。片言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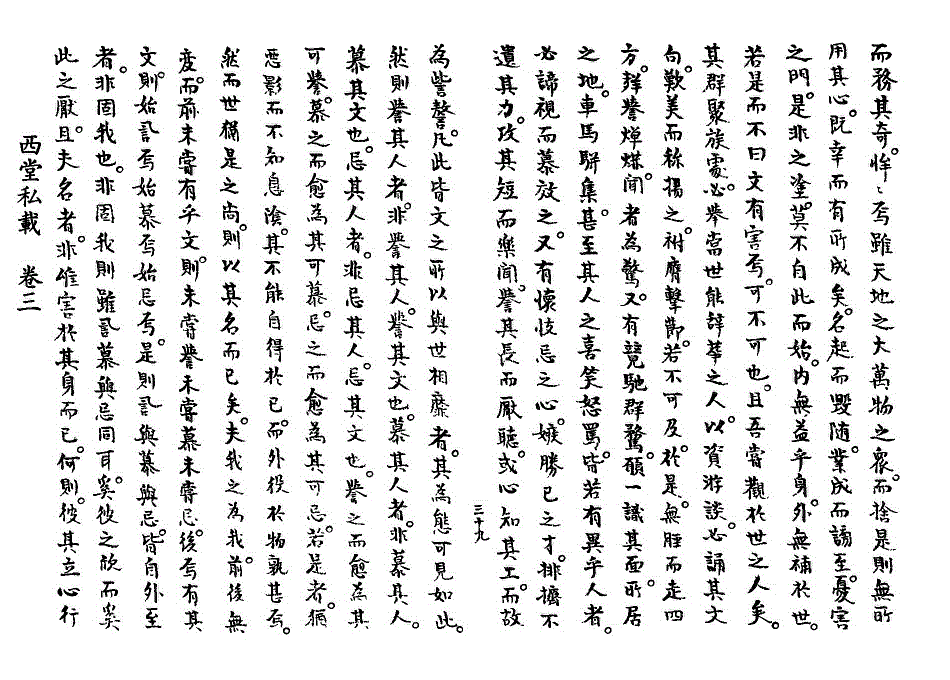 而务其奇。恈恈焉虽天地之大万物之众。而舍是则无所用其心。既幸而有所成矣。名起而毁随。业成而谤至。忧害之门。是非之涂。莫不自此而始。内无益乎身。外无补于世。若是而不曰文有害焉。可不可也。且吾尝观于世之人矣。其群聚族处。必举当世能辞华之人。以资游谈。必诵其文句。叹美而称扬之。祔膺击节。若不可及。于是。无胫而走四方。声誉燀赫。闻者为惊。又有竞驰群骛。愿一识其面。所居之地。车马骈集。甚至其人之喜笑怒骂。皆若有异乎人者。必谛视而慕效之。又有怀忮忌之心。嫉胜己之才。排挤不遗其力。攻其短而乐闻。誉其长而厌听。或心知其工。而故为訾謷。凡此皆文之所以与世相靡者。其为态可见如此。然则誉其人者。非誉其人。誉其文也。慕其人者。非慕其人。慕其文也。忌其人者。非忌其人。忌其文也。誉之而愈为其可誉。慕之而愈为其可慕。忌之而愈为其可忌。若是者。犹恶影而不知息阴。其不能自得于己。而外役于物孰甚焉。然而世犹是之尚。则以其名而已矣。夫我之为我。前后无变。而前未尝有乎文。则未尝誉未尝慕未尝忌。后焉有其文。则始誉焉始慕焉始忌焉。是则誉与慕与忌。皆自外至者。非固我也。非固我则虽誉慕与忌同耳。奚彼之欣而奚此之厌。且夫名者。非唯害于其身而已。何则。彼其立心行
而务其奇。恈恈焉虽天地之大万物之众。而舍是则无所用其心。既幸而有所成矣。名起而毁随。业成而谤至。忧害之门。是非之涂。莫不自此而始。内无益乎身。外无补于世。若是而不曰文有害焉。可不可也。且吾尝观于世之人矣。其群聚族处。必举当世能辞华之人。以资游谈。必诵其文句。叹美而称扬之。祔膺击节。若不可及。于是。无胫而走四方。声誉燀赫。闻者为惊。又有竞驰群骛。愿一识其面。所居之地。车马骈集。甚至其人之喜笑怒骂。皆若有异乎人者。必谛视而慕效之。又有怀忮忌之心。嫉胜己之才。排挤不遗其力。攻其短而乐闻。誉其长而厌听。或心知其工。而故为訾謷。凡此皆文之所以与世相靡者。其为态可见如此。然则誉其人者。非誉其人。誉其文也。慕其人者。非慕其人。慕其文也。忌其人者。非忌其人。忌其文也。誉之而愈为其可誉。慕之而愈为其可慕。忌之而愈为其可忌。若是者。犹恶影而不知息阴。其不能自得于己。而外役于物孰甚焉。然而世犹是之尚。则以其名而已矣。夫我之为我。前后无变。而前未尝有乎文。则未尝誉未尝慕未尝忌。后焉有其文。则始誉焉始慕焉始忌焉。是则誉与慕与忌。皆自外至者。非固我也。非固我则虽誉慕与忌同耳。奚彼之欣而奚此之厌。且夫名者。非唯害于其身而已。何则。彼其立心行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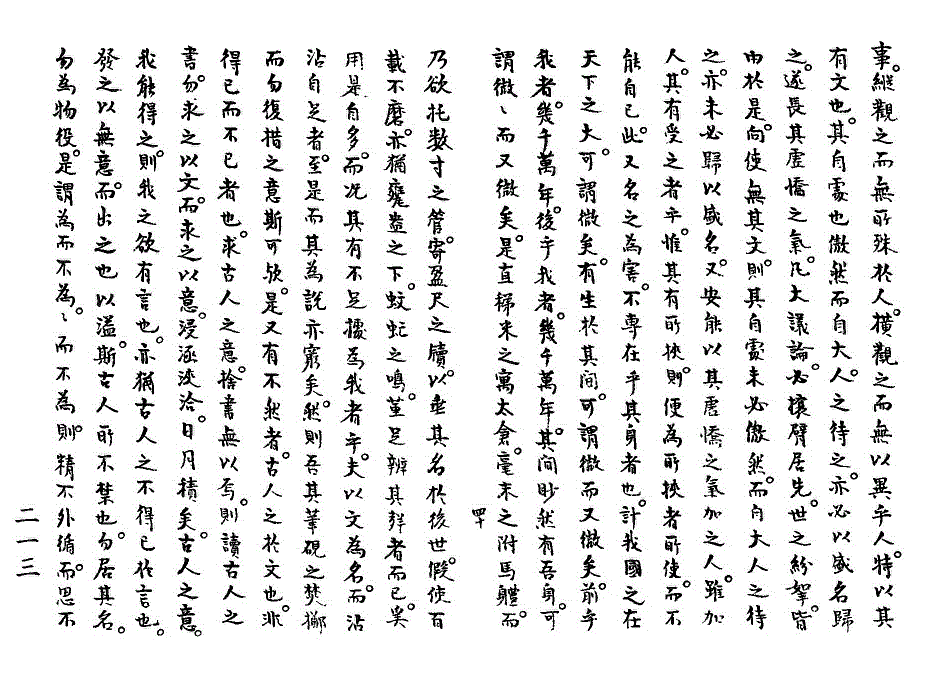 事。纵观之而无所殊于人。横观之而无以异乎人。特以其有文也。其自处也傲然而自大。人之待之。亦必以盛名归之。遂长其虚憍之气。凡大议论。必攘臂居先。世之纷挐。皆由于是。向使无其文。则其自处未必傲然。而自大人之待之。亦未必归以盛名。又安能以其虚憍之气加之人。虽加人。其有受之者乎。惟其有所挟。则便为所挟者所使。而不能自已。此又名之为害。不专在乎其身者也。计我国之在天下之大。可谓微矣。有生于其间。可谓微而又微矣。前乎我者。几千万年。后乎我者。几千万年。其间眇然有吾身。可谓微微而又微矣。是直稊米之寓太仓。毫末之附马体。而乃欲托数寸之管。寄盈尺之牍。以垂其名于后世。假使百载不磨。亦犹瓮盎之下。蚊虻之鸣。堇足辨其声者而已。奚用是自多。而况其有不足据为我者乎。夫以文为名。而沾沾自足者。至是而其为说亦穷矣。然则吾其笔砚之焚掷而勿复措之意斯可欤。是又有不然者。古人之于文也。非得已而不已者也。求古人之意。舍书无以焉。则读古人之书。勿求之以文。而求之以意。浸涵浃洽。日月积矣。古人之意。我能得之。则我之欲有言也。亦犹古人之不得已于言也。发之以无意。而出之也以溢。斯古人所不禁也。勿居其名。勿为物役。是谓为而不为。为而不为。则精不外循。而思不
事。纵观之而无所殊于人。横观之而无以异乎人。特以其有文也。其自处也傲然而自大。人之待之。亦必以盛名归之。遂长其虚憍之气。凡大议论。必攘臂居先。世之纷挐。皆由于是。向使无其文。则其自处未必傲然。而自大人之待之。亦未必归以盛名。又安能以其虚憍之气加之人。虽加人。其有受之者乎。惟其有所挟。则便为所挟者所使。而不能自已。此又名之为害。不专在乎其身者也。计我国之在天下之大。可谓微矣。有生于其间。可谓微而又微矣。前乎我者。几千万年。后乎我者。几千万年。其间眇然有吾身。可谓微微而又微矣。是直稊米之寓太仓。毫末之附马体。而乃欲托数寸之管。寄盈尺之牍。以垂其名于后世。假使百载不磨。亦犹瓮盎之下。蚊虻之鸣。堇足辨其声者而已。奚用是自多。而况其有不足据为我者乎。夫以文为名。而沾沾自足者。至是而其为说亦穷矣。然则吾其笔砚之焚掷而勿复措之意斯可欤。是又有不然者。古人之于文也。非得已而不已者也。求古人之意。舍书无以焉。则读古人之书。勿求之以文。而求之以意。浸涵浃洽。日月积矣。古人之意。我能得之。则我之欲有言也。亦犹古人之不得已于言也。发之以无意。而出之也以溢。斯古人所不禁也。勿居其名。勿为物役。是谓为而不为。为而不为。则精不外循。而思不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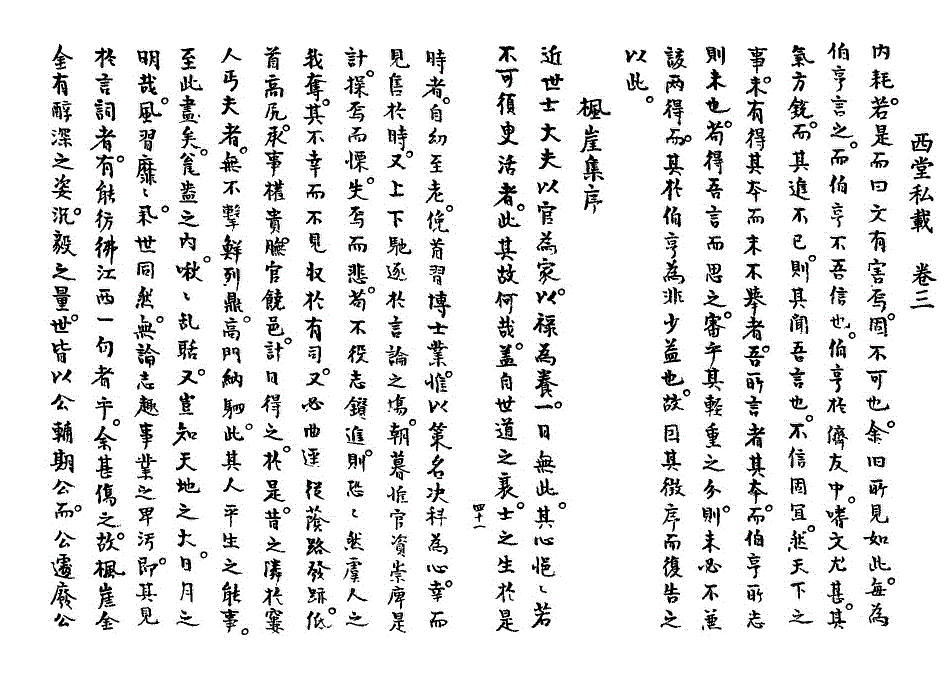 内耗。若是而曰文有害焉。固不可也。余旧所见如此。每为伯亨言之。而伯亨不吾信也。伯亨于侪友中。嗜文尤甚。其气方锐。而其进不已。则其闻吾言也。不信固宜。然天下之事。未有得其本而末不举者。吾所言者其本。而伯亨所志则未也。苟得吾言而思之。审乎其轻重之分。则未必不兼该两得。而其于伯亨为非少益也。故因其徵序而复告之以此。
内耗。若是而曰文有害焉。固不可也。余旧所见如此。每为伯亨言之。而伯亨不吾信也。伯亨于侪友中。嗜文尤甚。其气方锐。而其进不已。则其闻吾言也。不信固宜。然天下之事。未有得其本而末不举者。吾所言者其本。而伯亨所志则未也。苟得吾言而思之。审乎其轻重之分。则未必不兼该两得。而其于伯亨为非少益也。故因其徵序而复告之以此。枫崖集序
近世士大夫以官为家。以禄为养。一日无此。其心悒悒若不可须臾活者。此其故何哉。盖自世道之衰。士之生于是时者。自幼至老。俛首习博士业。惟以策名决科为心。幸而见售于时。又上下驰逐于言论之场。朝暮惟官资崇庳是计。操焉而慄。失焉而悲。苟不役志钻进。则恐恐然虞人之我夺。其不幸而不见收于有司。又必曲径从荫路发迹。低首高尻。承事权贵。膴官饶邑。计日得之。于是。昔之邻于窭人丐夫者。无不击鲜列鼎。高门纳驷。此其人平生之能事。至此尽矣。瓮盎之内。啾啾乱聒。又岂知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哉。风习靡靡。举世同然。无论志趣事业之卑污。即其见于言词者。有能彷佛江西一句者乎。余甚伤之。故枫崖金金(金衍字)有醇深之姿。沉毅之量。世皆以公辅期公。而公遽废公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4L 页
 车业。不屑就焉。则固已无求于世矣。及其连除内外职。尤闵闵如有所羞。多托病不起。其所俛就者堇数邑。而亦皆不久解归。归辄行橐萧然。不赍一物。惟阖户手一卷而已。家人或至丐贷举火。澹然不以营怀。其视世之逐逐利名者。不啻若浼己。盖公之胸襟。冲远夷旷。凡所谓得丧欣戚。无足以汩其天和。故其发于诗者。格高而气完。趣淡而意活。亦或往往因境见奇绝。无尖巧腐陈之病。推而为辞赋。为骈侣。俱精能天得。浏亮而有致。引物属辞。愈出愈工。一时词苑诸公。莫不敛衽推服。夫诗。所以言志。则志固言之本也。公之所以为本于平日者如此。故天机所动。㳷合声律。夫岂规规于椎(一作推)敲者所能及哉。公从子国舅庆恩公。尝以公所著。就先辈诸公。拣为三编。今金君后衍兄弟。以庆恩公之胤。遵庆恩公遗意。得芸阁铸字。印行公集。而问序于余。余窃尝闻公识虑弘深。论治道不拘细苛。务为恢广。简易。必援据经义。指陈成败。其绪言常谈。皆可师法。使公而有所施为于世。其必能救今日之坏败。不但超然于事物之外。如其所守而已也。惜时命不偶。使公阏于一第。终至落拓以终。斯岂独公之不幸。亦世道之不幸也。今其咳唾之馀。若又泯灭而无传。是重公之不遇。夫岂可哉。余与公居同巷。幼未省事。不及洒扫公门。以承绪论。每以为平
车业。不屑就焉。则固已无求于世矣。及其连除内外职。尤闵闵如有所羞。多托病不起。其所俛就者堇数邑。而亦皆不久解归。归辄行橐萧然。不赍一物。惟阖户手一卷而已。家人或至丐贷举火。澹然不以营怀。其视世之逐逐利名者。不啻若浼己。盖公之胸襟。冲远夷旷。凡所谓得丧欣戚。无足以汩其天和。故其发于诗者。格高而气完。趣淡而意活。亦或往往因境见奇绝。无尖巧腐陈之病。推而为辞赋。为骈侣。俱精能天得。浏亮而有致。引物属辞。愈出愈工。一时词苑诸公。莫不敛衽推服。夫诗。所以言志。则志固言之本也。公之所以为本于平日者如此。故天机所动。㳷合声律。夫岂规规于椎(一作推)敲者所能及哉。公从子国舅庆恩公。尝以公所著。就先辈诸公。拣为三编。今金君后衍兄弟。以庆恩公之胤。遵庆恩公遗意。得芸阁铸字。印行公集。而问序于余。余窃尝闻公识虑弘深。论治道不拘细苛。务为恢广。简易。必援据经义。指陈成败。其绪言常谈。皆可师法。使公而有所施为于世。其必能救今日之坏败。不但超然于事物之外。如其所守而已也。惜时命不偶。使公阏于一第。终至落拓以终。斯岂独公之不幸。亦世道之不幸也。今其咳唾之馀。若又泯灭而无传。是重公之不遇。夫岂可哉。余与公居同巷。幼未省事。不及洒扫公门。以承绪论。每以为平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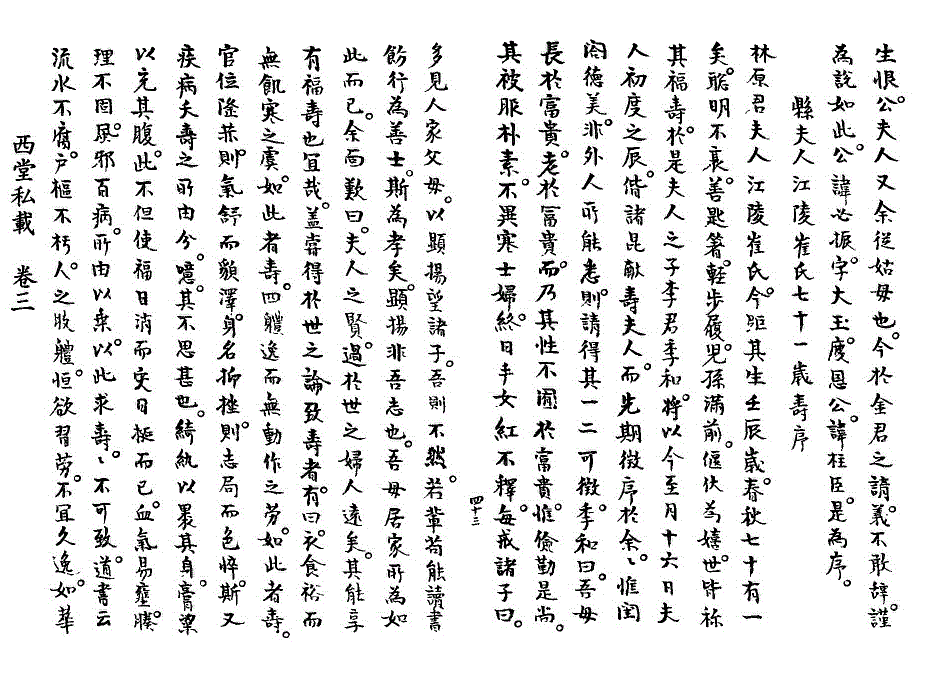 生恨。公夫人又余从姑母也。今于金君之请。义不敢辞。谨为说如此。公讳必振。字大玉。庆恩公。讳柱臣。是为序。
生恨。公夫人又余从姑母也。今于金君之请。义不敢辞。谨为说如此。公讳必振。字大玉。庆恩公。讳柱臣。是为序。县夫人江陵崔氏七十一岁寿序
林原君夫人江陵崔氏。今距其生壬辰岁。春秋七十有一矣。聪明不衰。善匙箸。轻步履。儿孙满前。偃伏为嬉。世皆称其福寿。于是夫人之子李君季和。将以今至月十六日夫人初度之辰。偕诸昆献寿夫人。而先期徵序于余。余惟闺閤德美。非外人所能悉。则请得其一二可徵。季和曰。吾母长于富贵。老于富贵。而乃其性不囿于富贵。惟俭勤是尚。其被服朴素。不异寒士妇。终日手女红不释。每戒诸子曰。多见人家父母。以显扬望诸子。吾则不然。若辈苟能读书饬行为善士。斯为孝矣。显扬非吾志也。吾母居家所为如此而已。余面叹曰。夫人之贤。过于世之妇人远矣。其能享有福寿也宜哉。盖尝得于世之论致寿者。有曰。衣食裕而无饥寒之虞。如此者寿。四体逸而无动作之劳。如此者寿。官位隆赫。则气舒而貌泽。身名抑挫。则志局而色悴。斯又疾病夭寿之所由分。噫。其不思甚也。绮纨以裹其身。膏粱以充其腹。此不但使福日消而灾日挻而已。血气易壅。腠理不固。风邪百病。所由以乘。以此求寿。寿不可致。道书云流水不腐。户枢不朽。人之肢体。恒欲习劳。不宜久逸。如华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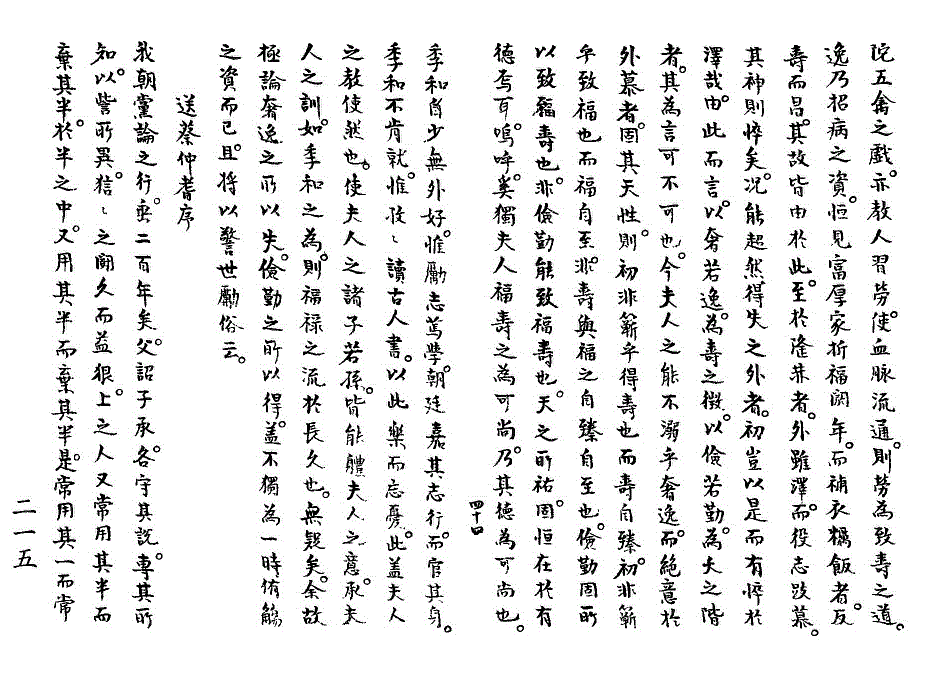 陀五禽之戏。亦教人习劳。使血脉流通。则劳为致寿之道。逸乃招病之资。恒见富厚家折福阏年。而补衣粝饭者。反寿而昌。其故皆由于此。至于隆赫者。外虽泽。而役志跂慕。其神则悴矣。况能超然于得失之外者。初岂以是而有悴泽哉。由此而言。以奢若逸。为寿之徵。以俭若勤。为夭之阶者。其为言可不可也。今夫人之能不溺乎奢逸。而绝意于外慕者。固其天性。则初非蕲乎得寿也而寿自臻。初非蕲乎致福也而福自至。非寿与福之自臻自至也。俭勤固所以致福寿也。非俭勤能致福寿也。天之所祐。固恒在于有德焉耳。呜呼。奚独夫人福寿之为可尚。乃其德为可尚也。季和自少无外好。惟励志笃学。朝廷嘉其志行。而官其身。季和不肯就。惟孜孜读古人书。以此乐而忘忧。此盖夫人之教使然也。使夫人之诸子若孙。皆能体夫人之意。承夫人之训。如季和之为。则福禄之流于长久也。无疑矣。余故极论奢逸之所以失。俭勤之所以得。盖不独为一时侑觞之资而已。且将以警世励俗云。
陀五禽之戏。亦教人习劳。使血脉流通。则劳为致寿之道。逸乃招病之资。恒见富厚家折福阏年。而补衣粝饭者。反寿而昌。其故皆由于此。至于隆赫者。外虽泽。而役志跂慕。其神则悴矣。况能超然于得失之外者。初岂以是而有悴泽哉。由此而言。以奢若逸。为寿之徵。以俭若勤。为夭之阶者。其为言可不可也。今夫人之能不溺乎奢逸。而绝意于外慕者。固其天性。则初非蕲乎得寿也而寿自臻。初非蕲乎致福也而福自至。非寿与福之自臻自至也。俭勤固所以致福寿也。非俭勤能致福寿也。天之所祐。固恒在于有德焉耳。呜呼。奚独夫人福寿之为可尚。乃其德为可尚也。季和自少无外好。惟励志笃学。朝廷嘉其志行。而官其身。季和不肯就。惟孜孜读古人书。以此乐而忘忧。此盖夫人之教使然也。使夫人之诸子若孙。皆能体夫人之意。承夫人之训。如季和之为。则福禄之流于长久也。无疑矣。余故极论奢逸之所以失。俭勤之所以得。盖不独为一时侑觞之资而已。且将以警世励俗云。送蔡仲耆序
我朝党论之行。垂二百年矣。父诏子承。各守其说。专其所知。以訾所异。狺狺之斗久而益狠。上之人又常用其半而弃其半。于半之中。又用其半而弃其半。是常用其一而常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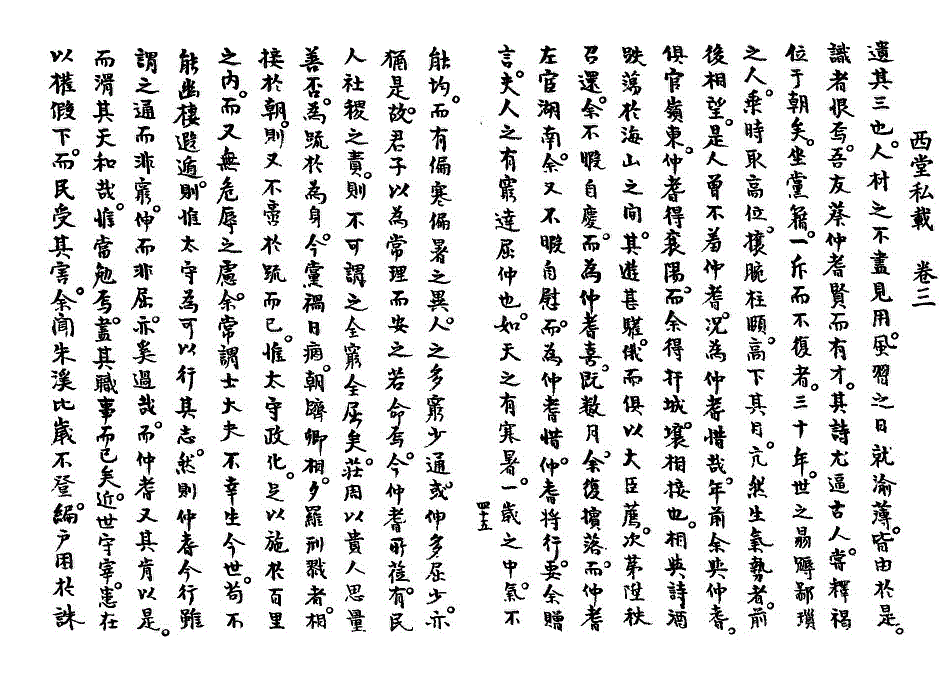 遗其三也。人材之不尽见用。风习之日就渝薄。皆由于是。识者恨焉。吾友蔡仲耆贤而有才。其诗尤逼古人。尝释褐位于朝矣。坐党籍。一斥而不复者。三十年。世之𦐇(一作傝)䢇鄙琐之人。乘时取高位。攘腕柱颐。高下其目。亢然生气势者。前后相望。是人曾不羞仲耆。况为仲耆惜哉。年前余与仲耆。俱官岭东。仲耆得襄阳。而余得捍城。壤相接也。相与诗酒跌荡于海山之间。其游甚驩。俄而俱以大臣荐。次第升秩召还。余不暇自庆。而为仲耆喜。既数月。余复摈落。而仲耆左宦湖南。余又不暇自慰。而为仲耆惜。仲耆将行。要余赠言。夫人之有穷达屈伸也。如天之有寒暑。一岁之中。气不能均。而有偏寒偏暑之异。人之多穷少通。或伸多屈少。亦犹是。故君子以为常理而安之若命焉。今仲耆所莅。有民人社稷之责。则不可谓之全穷全屈矣。庄周以贵人思量善否。为疏于为身。今党祸日痼。朝跻卿相。夕罗刑戮者。相接于朝。则又不啻于疏而已。惟太守政化。足以施于百里之内。而又无危辱之虑。余常谓士大夫不幸生今世。苟不能幽栖遐遁。则惟太守为可以行其志。然则仲耆今行虽谓之通而非穷。伸而非屈。亦奚过哉。而仲耆又其肯以是。而滑其天和哉。惟当勉焉。尽其职事而已矣。近世守宰。患在以权假下。而民受其害。余闻朱溪比岁不登。编户困于诛
遗其三也。人材之不尽见用。风习之日就渝薄。皆由于是。识者恨焉。吾友蔡仲耆贤而有才。其诗尤逼古人。尝释褐位于朝矣。坐党籍。一斥而不复者。三十年。世之𦐇(一作傝)䢇鄙琐之人。乘时取高位。攘腕柱颐。高下其目。亢然生气势者。前后相望。是人曾不羞仲耆。况为仲耆惜哉。年前余与仲耆。俱官岭东。仲耆得襄阳。而余得捍城。壤相接也。相与诗酒跌荡于海山之间。其游甚驩。俄而俱以大臣荐。次第升秩召还。余不暇自庆。而为仲耆喜。既数月。余复摈落。而仲耆左宦湖南。余又不暇自慰。而为仲耆惜。仲耆将行。要余赠言。夫人之有穷达屈伸也。如天之有寒暑。一岁之中。气不能均。而有偏寒偏暑之异。人之多穷少通。或伸多屈少。亦犹是。故君子以为常理而安之若命焉。今仲耆所莅。有民人社稷之责。则不可谓之全穷全屈矣。庄周以贵人思量善否。为疏于为身。今党祸日痼。朝跻卿相。夕罗刑戮者。相接于朝。则又不啻于疏而已。惟太守政化。足以施于百里之内。而又无危辱之虑。余常谓士大夫不幸生今世。苟不能幽栖遐遁。则惟太守为可以行其志。然则仲耆今行虽谓之通而非穷。伸而非屈。亦奚过哉。而仲耆又其肯以是。而滑其天和哉。惟当勉焉。尽其职事而已矣。近世守宰。患在以权假下。而民受其害。余闻朱溪比岁不登。编户困于诛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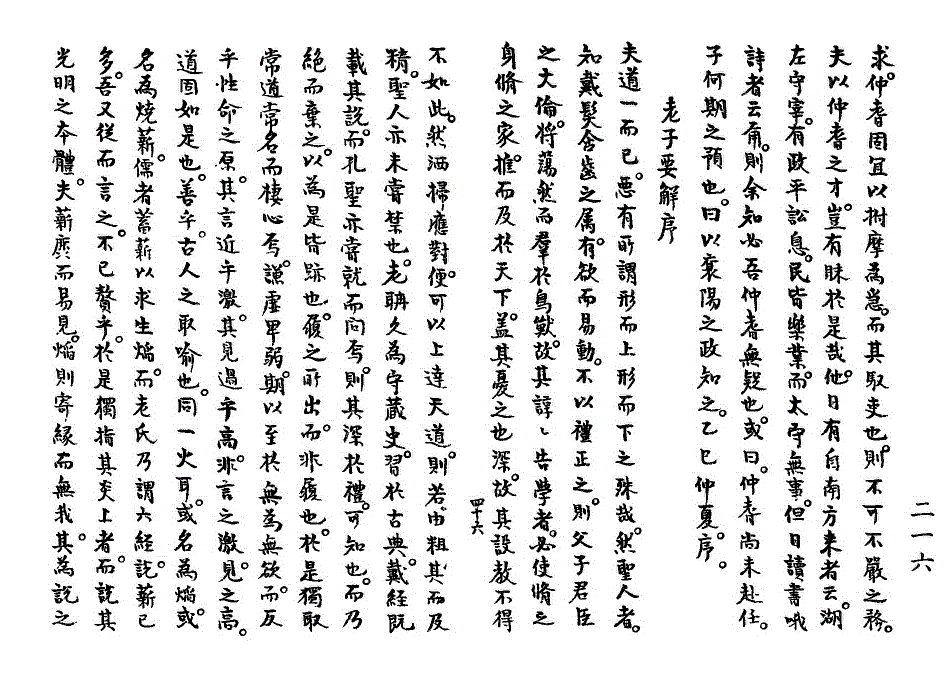 求。仲耆固宜以拊摩为急。而其驭吏也。则不可不严之务。夫以仲耆之才。岂有眛于是哉。他日有自南方来者云。湖左守宰。有政平讼息。民皆乐业。而太守无事。但日读书哦诗者云尔。则余知必吾仲耆无疑也。或曰。仲耆尚未赴任。子何期之预也。曰以襄阳之政知之。乙巳仲夏。序。
求。仲耆固宜以拊摩为急。而其驭吏也。则不可不严之务。夫以仲耆之才。岂有眛于是哉。他日有自南方来者云。湖左守宰。有政平讼息。民皆乐业。而太守无事。但日读书哦诗者云尔。则余知必吾仲耆无疑也。或曰。仲耆尚未赴任。子何期之预也。曰以襄阳之政知之。乙巳仲夏。序。老子要解序
夫道一而已。恶有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之殊哉。然圣人者。知戴发含齿之属。有欲而易动。不以礼正之。则父子君臣之大伦。将荡然而群于鸟兽。故其谆谆告学者。必使脩之身脩之家。推而及于天下。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设教不得不如此。然洒扫应对。便可以上达天道。则若其由粗而及精。圣人亦未尝禁也。老聃久为守藏史。习于古典。戴经既载其说。而孔圣亦尝就而问焉。则其深于礼。可知也。而乃绝而弃之。以为是皆迹也。履之所出。而非履也。于是独取常道常名而栖心焉。谦虚卑弱。期以至于无为无欲。而反乎性命之原。其言近乎激。其见过乎高。非言之激。见之高。道固如是也。善乎。古人之取喻也。同一火耳。或名为焰。或名为烧薪。儒者蓄薪以求生焰。而老氏乃谓六经。说薪已多。吾又从而言之。不已赘乎。于是独指其炎上者。而说其光明之本体。夫薪粗而易见。焰则寄缘而无我。其为说之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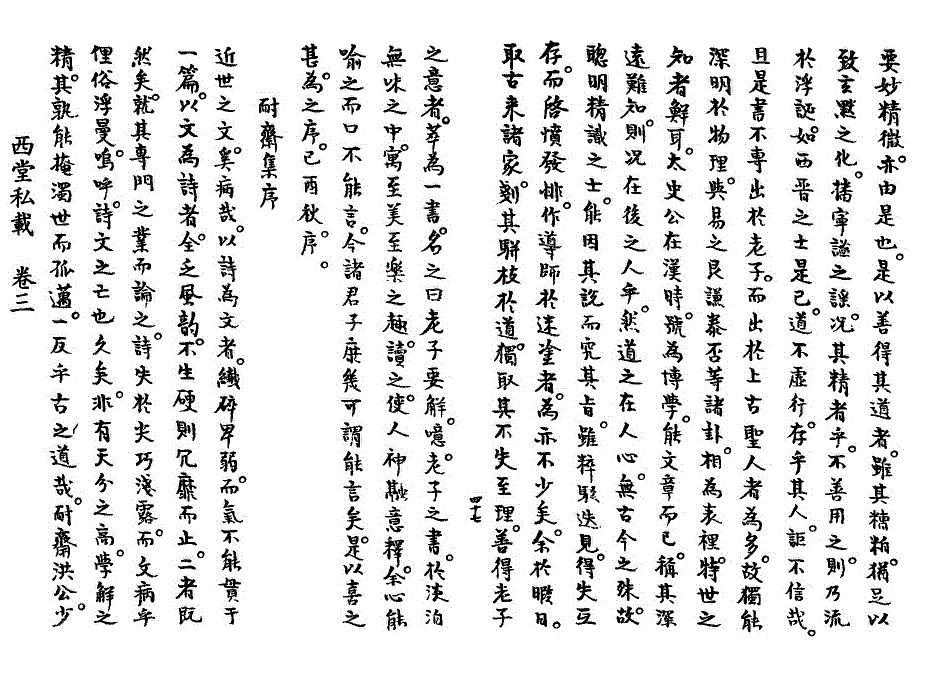 要妙精微。亦由是也。是以善得其道者。虽其糟粕。犹足以致玄默之化。播宁谧之谣。况其精者乎。不善用之。则乃流于浮诞。如西晋之士是已。道不虚行。存乎其人。讵不信哉。且是书不专出于老子。而出于上古圣人者为多。故独能深明于物理。与易之艮谦泰否等诸卦。相为表里。特世之知者鲜耳。太史公在汉时。号为博学。能文章而已。称其深远难知。则况在后之人乎。然道之在人心。无古今之殊。故聪明精识之士。能因其说而究其旨。虽粹驳迭见。得失互存。而启愤发悱。作导师于迷涂者。为亦不少矣。余于暇日。取古来诸家。刬其骈枝于道。独取其不失至理。善得老子之意者。萃为一书。名之曰老子要解。噫。老子之书。于淡泊无味之中。寓至美至乐之趣。读之。使人神融意释。余心能喻之而口不能言。今诸君子庶几可谓能言矣。是以喜之甚。为之序。己酉秋。序。
要妙精微。亦由是也。是以善得其道者。虽其糟粕。犹足以致玄默之化。播宁谧之谣。况其精者乎。不善用之。则乃流于浮诞。如西晋之士是已。道不虚行。存乎其人。讵不信哉。且是书不专出于老子。而出于上古圣人者为多。故独能深明于物理。与易之艮谦泰否等诸卦。相为表里。特世之知者鲜耳。太史公在汉时。号为博学。能文章而已。称其深远难知。则况在后之人乎。然道之在人心。无古今之殊。故聪明精识之士。能因其说而究其旨。虽粹驳迭见。得失互存。而启愤发悱。作导师于迷涂者。为亦不少矣。余于暇日。取古来诸家。刬其骈枝于道。独取其不失至理。善得老子之意者。萃为一书。名之曰老子要解。噫。老子之书。于淡泊无味之中。寓至美至乐之趣。读之。使人神融意释。余心能喻之而口不能言。今诸君子庶几可谓能言矣。是以喜之甚。为之序。己酉秋。序。耐斋集序
近世之文。奚病哉。以诗为文者。纤碎卑弱。而气不能贯于一篇。以文为诗者。全乏风韵。不生硬则冗靡而止。二者既然矣。就其专门之业而论之。诗失于尖巧浅露。而文病乎俚俗浮曼。呜呼。诗文之亡也久矣。非有天分之高。学解之精。其孰能掩浊世而孤迈。一反乎古之道哉。耐斋洪公。少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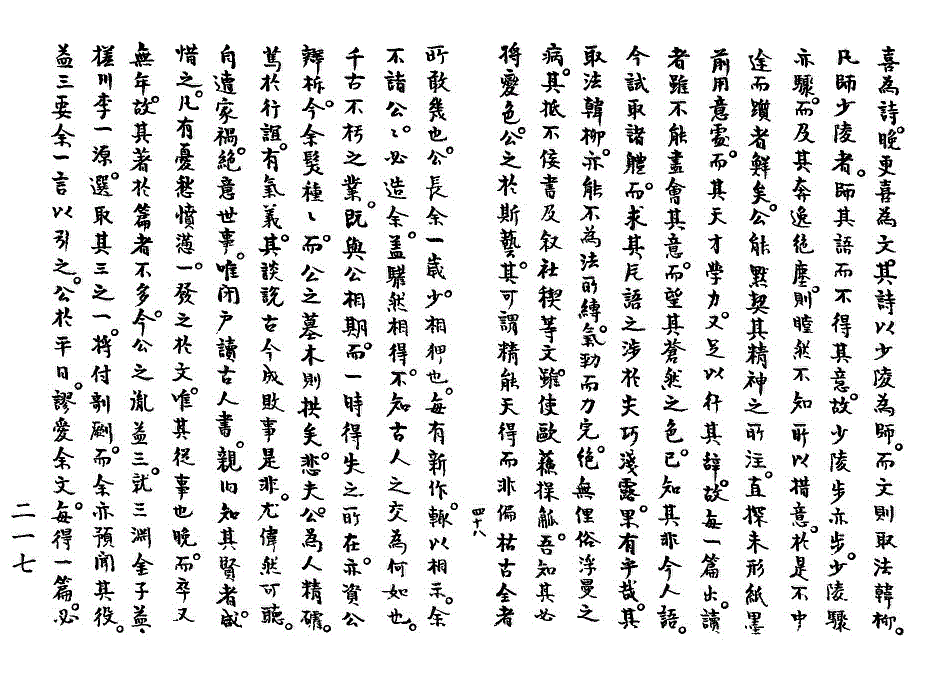 喜为诗。晚更喜为文。其诗以少陵为师。而文则取法韩柳。凡师少陵者。师其语而不得其意。故少陵步亦步。少陵骤亦骤。而及其奔逸绝尘。则瞠然不知所以措意。于是不中途而踬者鲜矣。公能默契其精神之所注。直探未形纸墨前用意处。而其天才学力。又足以行其辞。故每一篇出。读者虽不能尽会其意。而望其苍然之色。已知其非今人语。今试取诸体。而求其片语之涉于尖巧浅露。果有乎哉。其取法韩柳。亦能不为法所缚。气劲而力完。绝无俚俗浮曼之病。其抵不佞书及叙社稧等文。虽使欧苏操觚。吾知其必将变色。公之于斯艺。其可谓精能天得而非偏枯古全者所敢几也。公长余一岁。少相狎也。每有新作。辄以相示。余不诣公。公必造余。盖驩然相得。不知古人之交为何如也。千古不朽之业。既与公相期。而一时得失之所在。亦资公辩析。今余发种种。而公之墓木则拱矣。悲夫。公为人精礭。笃于行谊。有气义。其谈说古今成败事是非。尤伟然可听。自遭家祸。绝意世事。唯闭户读古人书。亲旧知其贤者。咸惜之。凡有忧愁愤懑。一发之于文。唯其从事也晚。而卒又无年。故其著于篇者不多。今公之胤益三。就三渊金子益,槎川李一源。选取其三之一。将付剞劂。而余亦预闻其役。益三要余一言以引之。公于平日。谬爱余文。每得一篇。必
喜为诗。晚更喜为文。其诗以少陵为师。而文则取法韩柳。凡师少陵者。师其语而不得其意。故少陵步亦步。少陵骤亦骤。而及其奔逸绝尘。则瞠然不知所以措意。于是不中途而踬者鲜矣。公能默契其精神之所注。直探未形纸墨前用意处。而其天才学力。又足以行其辞。故每一篇出。读者虽不能尽会其意。而望其苍然之色。已知其非今人语。今试取诸体。而求其片语之涉于尖巧浅露。果有乎哉。其取法韩柳。亦能不为法所缚。气劲而力完。绝无俚俗浮曼之病。其抵不佞书及叙社稧等文。虽使欧苏操觚。吾知其必将变色。公之于斯艺。其可谓精能天得而非偏枯古全者所敢几也。公长余一岁。少相狎也。每有新作。辄以相示。余不诣公。公必造余。盖驩然相得。不知古人之交为何如也。千古不朽之业。既与公相期。而一时得失之所在。亦资公辩析。今余发种种。而公之墓木则拱矣。悲夫。公为人精礭。笃于行谊。有气义。其谈说古今成败事是非。尤伟然可听。自遭家祸。绝意世事。唯闭户读古人书。亲旧知其贤者。咸惜之。凡有忧愁愤懑。一发之于文。唯其从事也晚。而卒又无年。故其著于篇者不多。今公之胤益三。就三渊金子益,槎川李一源。选取其三之一。将付剞劂。而余亦预闻其役。益三要余一言以引之。公于平日。谬爱余文。每得一篇。必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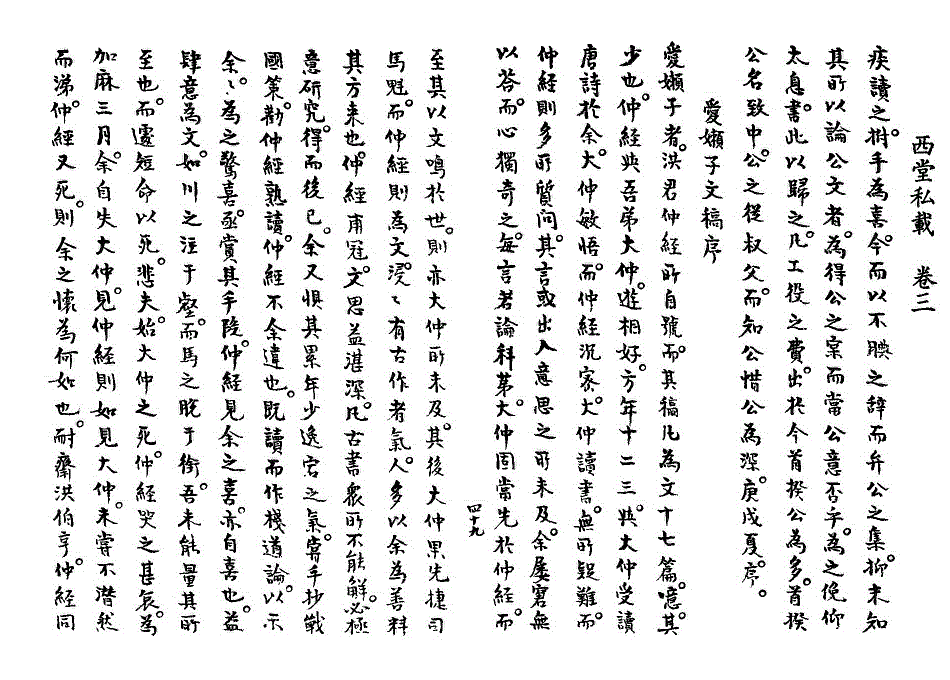 疾读之。拊手为喜。今而以不腆之辞而弁公之集。抑未知其所以论公文者。为得公之实而当公意否乎。为之俛仰太息。书此以归之。凡工役之费。出于今首揆公为多。首揆公名致中。公之从叔父。而知公惜公为深。庚戌夏。序。
疾读之。拊手为喜。今而以不腆之辞而弁公之集。抑未知其所以论公文者。为得公之实而当公意否乎。为之俛仰太息。书此以归之。凡工役之费。出于今首揆公为多。首揆公名致中。公之从叔父。而知公惜公为深。庚戌夏。序。爱懒子文稿序
爱懒子者。洪君仲经所自号。而其稿凡为文十七篇。噫。其少也。仲经与吾弟大仲。游相好。方年十二三。与大仲受读唐诗于余。大仲敏悟。而仲经沉密。大仲读书。无所疑难。而仲经则多所质问。其言或出入意思之所未及。余屡窘无以答。而心独奇之。每言若论科第。大仲固当先于仲经。而至其以文鸣于世。则亦大仲所未及。其后大仲果先捷司马魁。而仲经则为文。浸浸有古作者气。人多以余为善料其方来也。仲经甫冠。文思益湛深。凡古书众所不能解。必极意研究。得而后已。余又惧其累年少逸宕之气。尝手抄战国策。劝仲经熟读。仲经不余违也。既读而作栈道论。以示余。余为之惊喜。亟赏其手段。仲经见余之喜。亦自喜也。益肆意为文。如川之注于壑。而马之脱于衔。吾未能量其所至也。而遽短命以死。悲夫。始大仲之死。仲经哭之甚哀。为加麻三月。余自失大仲。见仲经则如见大仲。未尝不潜然而涕。仲经又死。则余之怀为何如也。耐斋洪伯亨。仲经同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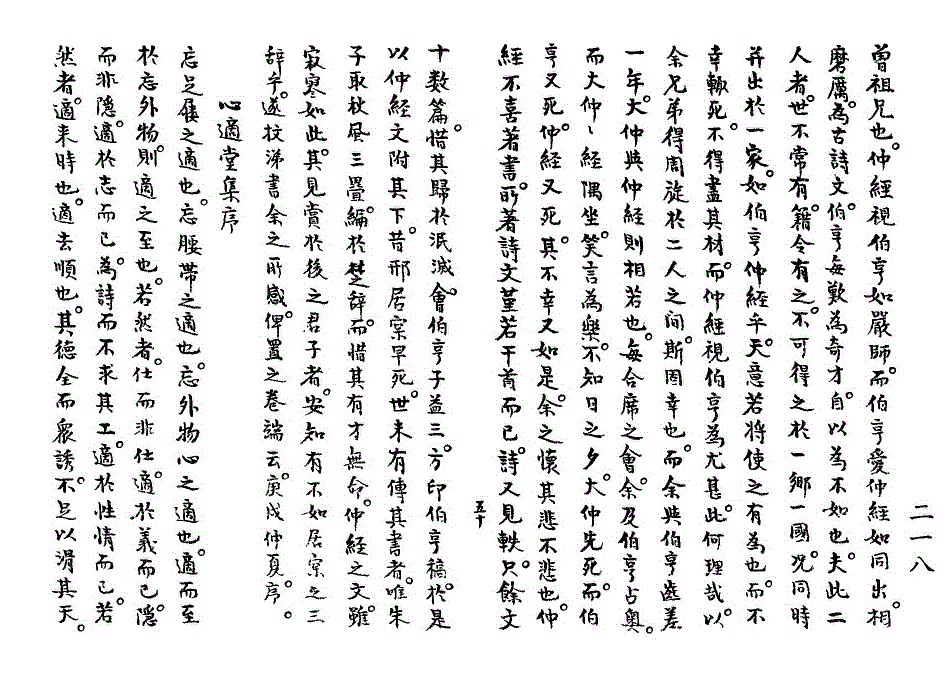 曾祖兄也。仲经视伯亨如严师。而伯亨爱仲经如同出。相磨厉。为古诗文。伯亨每叹为奇才。自以为不如也。夫此二人者。世不常有。籍令有之。不可得之于一乡一国。况同时并出于一家。如伯亨仲经乎。天意若将使之有为也。而不幸辄死。不得尽其材。而仲经视伯亨为尤甚。此何理哉。以余兄弟得周旋于二人之间。斯固幸也。而余与伯亨齿差一年。大仲与仲经则相若也。每合席之会。余及伯亨占奥。而大仲仲经隅坐。笑言为乐。不知日之夕。大仲先死。而伯亨又死。仲经又死。其不幸又如是。余之怀其悲不悲也。仲经不喜著书。所著诗文堇若干首而已。诗又见轶。只馀文十数篇。惜其归于泯灭。会伯亨子益三。方印伯亨稿。于是以仲经文附其下。昔邢居实早死。世未有传其书者。唯朱子取秋风三叠。编于楚辞。而惜其有才无命。仲经之文。虽寂寥如此。其见赏于后之君子者。安知有不如居实之三辞乎。遂抆涕书余之所感。俾置之卷端云。庚戌仲夏。序。
曾祖兄也。仲经视伯亨如严师。而伯亨爱仲经如同出。相磨厉。为古诗文。伯亨每叹为奇才。自以为不如也。夫此二人者。世不常有。籍令有之。不可得之于一乡一国。况同时并出于一家。如伯亨仲经乎。天意若将使之有为也。而不幸辄死。不得尽其材。而仲经视伯亨为尤甚。此何理哉。以余兄弟得周旋于二人之间。斯固幸也。而余与伯亨齿差一年。大仲与仲经则相若也。每合席之会。余及伯亨占奥。而大仲仲经隅坐。笑言为乐。不知日之夕。大仲先死。而伯亨又死。仲经又死。其不幸又如是。余之怀其悲不悲也。仲经不喜著书。所著诗文堇若干首而已。诗又见轶。只馀文十数篇。惜其归于泯灭。会伯亨子益三。方印伯亨稿。于是以仲经文附其下。昔邢居实早死。世未有传其书者。唯朱子取秋风三叠。编于楚辞。而惜其有才无命。仲经之文。虽寂寥如此。其见赏于后之君子者。安知有不如居实之三辞乎。遂抆涕书余之所感。俾置之卷端云。庚戌仲夏。序。心适堂集序
忘足屦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忘外物心之适也。适而至于忘外物。则适之至也。若然者。仕而非仕。适于义而已。隐而非隐。适于志而已。为诗而不求其工。适于性情而已。若然者。适来时也。适去顺也。其德全而众诱。不足以滑其天。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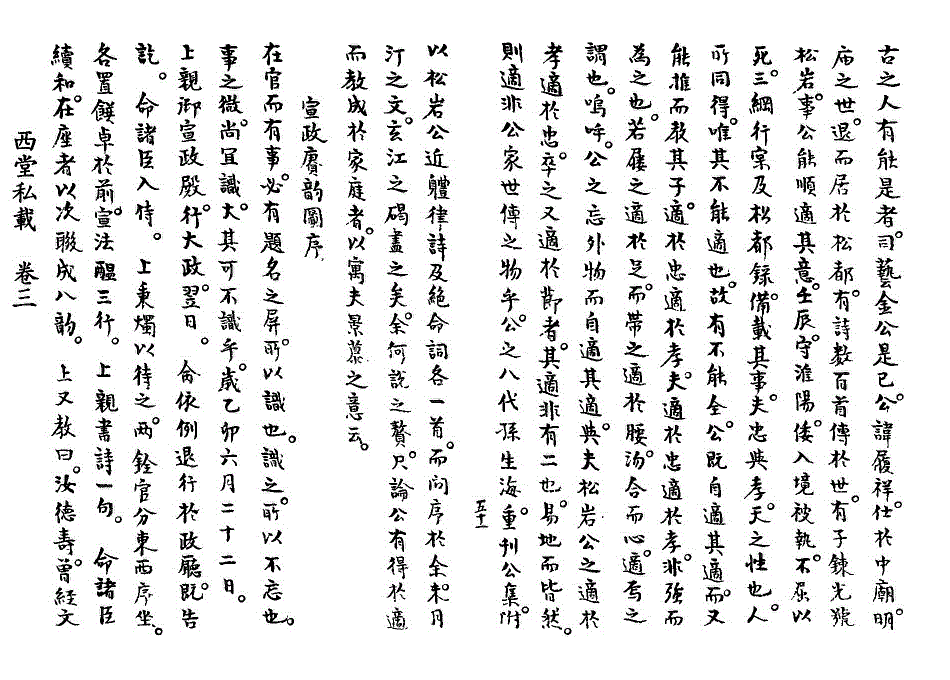 古之人有能是者。司艺金公是已。公讳履祥。仕于中庙。明庙之世。退而居于松都。有诗数百首传于世。有子鍊光号松岩。事公能顺适其意。壬辰。守淮阳。倭入境被执。不屈以死。三纲行实及松都录。备载其事。夫忠与孝。天之性也。人所同得。唯其不能适也。故有不能全。公既自适其适。而又能推而教其子。适于忠适于孝。夫适于忠适于孝。非强而为之也。若屦之适于足。而带之适于腰。沕(一作吻)合而心。适焉之谓也。呜呼。公之忘外物而自适其适。与夫松岩公之适于孝适于忠。卒之又适于节者。其适非有二也。易地而皆然。则适非公家世传之物乎。公之八代孙生海。重刊公集。附以松岩公近体律诗及绝命词各一首。而问序于余。未月汀之文。玄江之碣尽之矣。余何说之赘。只论公有得于适而教成于家庭者。以寓夫景慕之意云。
古之人有能是者。司艺金公是已。公讳履祥。仕于中庙。明庙之世。退而居于松都。有诗数百首传于世。有子鍊光号松岩。事公能顺适其意。壬辰。守淮阳。倭入境被执。不屈以死。三纲行实及松都录。备载其事。夫忠与孝。天之性也。人所同得。唯其不能适也。故有不能全。公既自适其适。而又能推而教其子。适于忠适于孝。夫适于忠适于孝。非强而为之也。若屦之适于足。而带之适于腰。沕(一作吻)合而心。适焉之谓也。呜呼。公之忘外物而自适其适。与夫松岩公之适于孝适于忠。卒之又适于节者。其适非有二也。易地而皆然。则适非公家世传之物乎。公之八代孙生海。重刊公集。附以松岩公近体律诗及绝命词各一首。而问序于余。未月汀之文。玄江之碣尽之矣。余何说之赘。只论公有得于适而教成于家庭者。以寓夫景慕之意云。宣政赓韵图序
在官而有事。必有题名之屏。所以识也。识之。所以不忘也。事之微。尚宜识。大其可不识乎。岁乙卯六月二十二日。 上亲御宣政殿。行大政。翌日。 命依例退行于政厅。既告讫。 命诸臣入侍。 上秉烛以待之。两铨官分东西序坐。各置馔卓于前。宣法酝三行。 上亲书诗一句。 命诸臣续和。在座者以次联成八韵。 上又教曰。汝德寿。曾经文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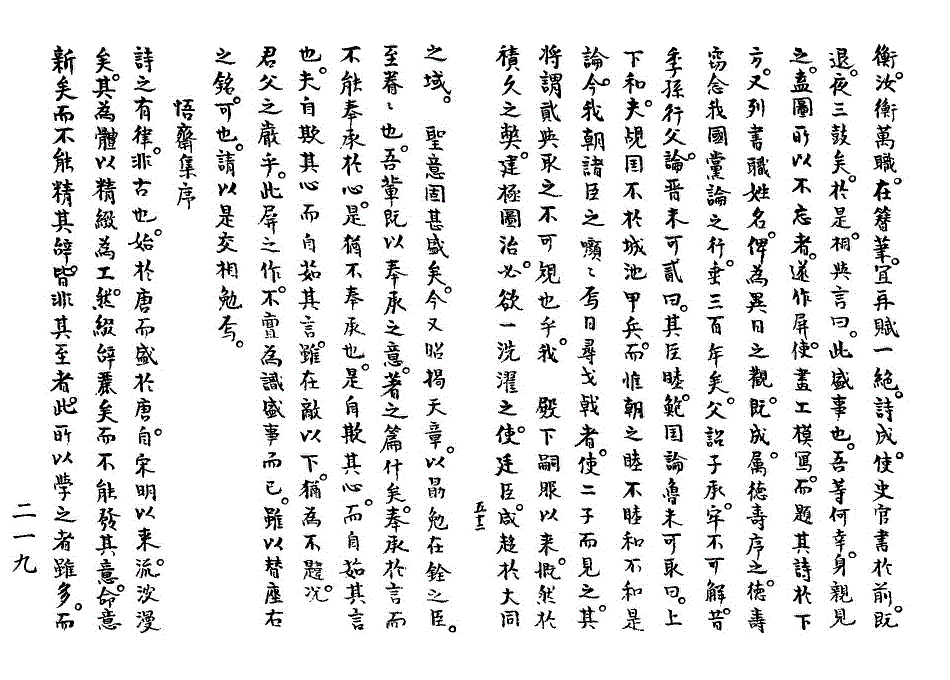 衡。汝衡万职。在簪笔。宜再赋一绝。诗成。使史官书于前。既退。夜三鼓矣。于是。相与言曰。此盛事也。吾等何幸。身亲见之。盍图所以不忘者。遂作屏。使画工模写。而题其诗于下方。又列书职姓名。俾为异日之观。既成。属德寿序之。德寿窃念我国党论之行。垂三百年矣。父诏子承。牢不可解。昔季孙行父。论晋未可贰曰。其臣睦。鲍国论鲁未可取曰。上下和。夫觇国不于城池甲兵。而惟朝之睦不睦和不和是论。今我朝诸臣之㘖㘖焉日寻戈戟者。使二子而见之。其将谓贰与取之不可观也乎。我 殿下嗣服以来。慨然于积久之弊。建极图治。必欲一洗濯之。使廷臣。咸趍于大同之域。 圣意固甚盛矣。今又昭揭天章。以勖勉在铨之臣。至眷眷也。吾辈既以奉承之意。著之篇什矣。奉承于言而不能奉承于心。是犹不奉承也。是自欺其心。而自茹其言也。夫自欺其心而自茹其言。虽在敌以下。犹为不韪。况 君父之严乎。此屏之作。不亶为识盛事而已。虽以替座右之铭。可也。请以是交相勉焉。
衡。汝衡万职。在簪笔。宜再赋一绝。诗成。使史官书于前。既退。夜三鼓矣。于是。相与言曰。此盛事也。吾等何幸。身亲见之。盍图所以不忘者。遂作屏。使画工模写。而题其诗于下方。又列书职姓名。俾为异日之观。既成。属德寿序之。德寿窃念我国党论之行。垂三百年矣。父诏子承。牢不可解。昔季孙行父。论晋未可贰曰。其臣睦。鲍国论鲁未可取曰。上下和。夫觇国不于城池甲兵。而惟朝之睦不睦和不和是论。今我朝诸臣之㘖㘖焉日寻戈戟者。使二子而见之。其将谓贰与取之不可观也乎。我 殿下嗣服以来。慨然于积久之弊。建极图治。必欲一洗濯之。使廷臣。咸趍于大同之域。 圣意固甚盛矣。今又昭揭天章。以勖勉在铨之臣。至眷眷也。吾辈既以奉承之意。著之篇什矣。奉承于言而不能奉承于心。是犹不奉承也。是自欺其心。而自茹其言也。夫自欺其心而自茹其言。虽在敌以下。犹为不韪。况 君父之严乎。此屏之作。不亶为识盛事而已。虽以替座右之铭。可也。请以是交相勉焉。悟斋集序
诗之有律。非古也。始于唐而盛于唐。自宋明以来。流波漫矣。其为体以精致为工。然缀辞丽矣而不能发其意。命意新矣而不能精其辞。皆非其至者。此所以学之者虽多。而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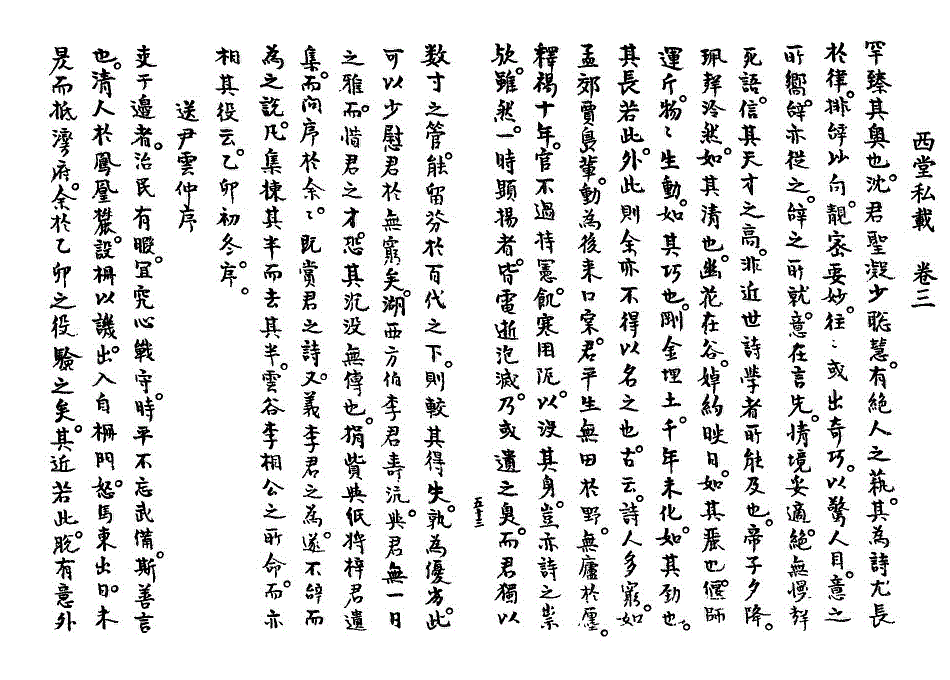 罕臻其奥也。沈君圣凝少聪慧。有绝人之萟。其为诗尤长于律。排辞比句。靓密要妙。往往或出奇巧。以惊人目。意之所向。辞亦从之。辞之所就。意在言先。情境妥适。绝无慢声死语。信其天才之高。非近世诗学者所能及也。帝子夕降。佩声泠然。如其清也。幽花在谷。婥约映日。如其丽也。偃师运斤。物物生动。如其巧也。刚金埋土。千年未化。如其劲也。其长若此。外此则余亦不得以名之也。古云。诗人多穷。如孟郊贾岛辈。动为后来口实。君平生无田于野。无庐于廛。释褐十年。官不过持宪。饥寒困阨。以没其身。岂亦诗之祟欤。虽然。一时显扬者。皆电逝泡灭。乃或遗之臭。而君独以数寸之管。能留芬于百代之下。则较其得失。孰为优劣。此可以少慰君于无穷矣。湖西方伯李君寿沆。与君无一日之雅。而惜君之才。恐其沉没无传也。捐赀与纸将梓君遗集。而问序于余。余既赏君之诗。又义李君之为。遂不辞而为之说。凡集拣其半而去其半。云谷李相公之所命。而亦相其役云。乙卯初冬。序。
罕臻其奥也。沈君圣凝少聪慧。有绝人之萟。其为诗尤长于律。排辞比句。靓密要妙。往往或出奇巧。以惊人目。意之所向。辞亦从之。辞之所就。意在言先。情境妥适。绝无慢声死语。信其天才之高。非近世诗学者所能及也。帝子夕降。佩声泠然。如其清也。幽花在谷。婥约映日。如其丽也。偃师运斤。物物生动。如其巧也。刚金埋土。千年未化。如其劲也。其长若此。外此则余亦不得以名之也。古云。诗人多穷。如孟郊贾岛辈。动为后来口实。君平生无田于野。无庐于廛。释褐十年。官不过持宪。饥寒困阨。以没其身。岂亦诗之祟欤。虽然。一时显扬者。皆电逝泡灭。乃或遗之臭。而君独以数寸之管。能留芬于百代之下。则较其得失。孰为优劣。此可以少慰君于无穷矣。湖西方伯李君寿沆。与君无一日之雅。而惜君之才。恐其沉没无传也。捐赀与纸将梓君遗集。而问序于余。余既赏君之诗。又义李君之为。遂不辞而为之说。凡集拣其半而去其半。云谷李相公之所命。而亦相其役云。乙卯初冬。序。送尹云仲序
吏于边者。治民有暇。宜究心战守。时平不忘武备。斯善言也。清人于凤凰麓。设栅以讥。出入自栅门。怒马东出。日未昃而抵湾府。余于乙卯之役验之矣。其近若此。脱有意外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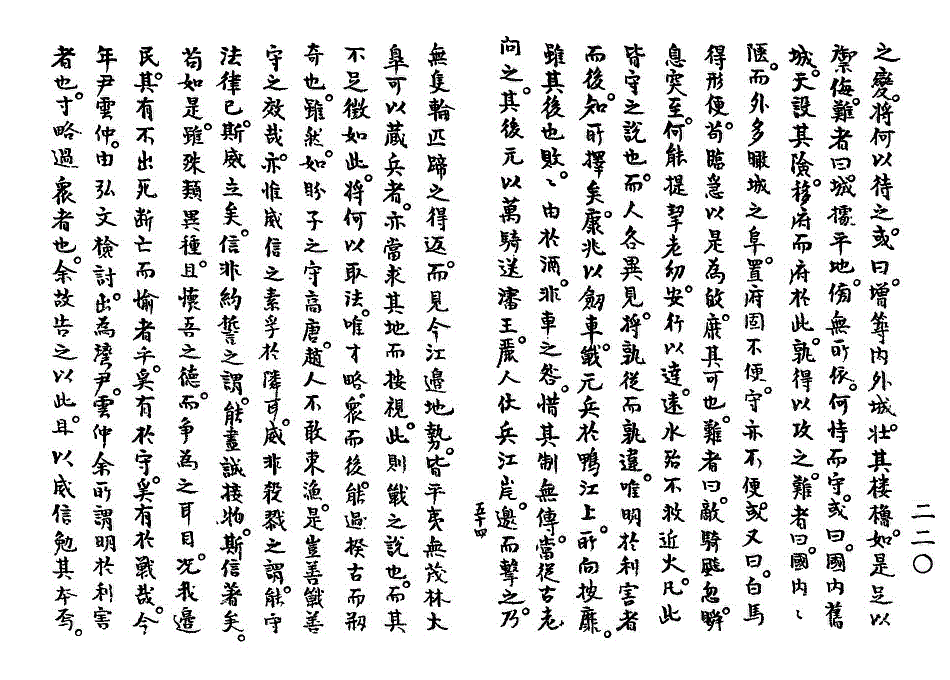 之变。将何以待之。或曰。增筑内外城。壮其楼橹。如是足以御侮。难者曰。城据平地。傍无所依。何恃而守。或曰。国内旧城。天设其险。移府而府于此。孰得以攻之。难者曰。国内内狭。而外多瞰城之阜。置府固不便。守亦不便。或又曰。白马得形便。苟临急以是为敀。庶其可也。难者曰。敌骑飙忽。瞬息突至。何能提挈老幼。安行以达。远水殆不救近火。凡此皆守之说也。而人各异见。将孰从而孰违。唯明于利害者而后。知所择矣。康兆以剑车。战元兵于鸭江上。所向披靡。虽其后也败。败由于酒。非车之咎。惜其制无传。当从古老问之。其后元以万骑送沈王。丽人伏兵江岸。邀而击之。乃无只轮匹蹄之得返。而见今江边地势。皆平夷无茂林大皋可以藏兵者。亦当求其地而按视。此则战之说也。而其不足徵如此。将何以取法。唯才略过众而后。能揆古而刱奇也。虽然。如盼子之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是岂善战善守之效哉。亦惟威信之素孚于邻耳。威非杀戮之谓。能守法律已。斯威立矣。信非约誓之谓。能尽诚接物。斯信著矣。苟如是。虽殊类异种。且怀吾之德。而争为之耳目。况我边民。其有不出死断亡而愉者乎。奚有于守。奚有于战哉。今年尹云仲。由弘文检讨。出为湾尹。云仲余所谓明于利害者也。寸(一作才)略过众者也。余故告之以此。且以威信勉其本焉。
之变。将何以待之。或曰。增筑内外城。壮其楼橹。如是足以御侮。难者曰。城据平地。傍无所依。何恃而守。或曰。国内旧城。天设其险。移府而府于此。孰得以攻之。难者曰。国内内狭。而外多瞰城之阜。置府固不便。守亦不便。或又曰。白马得形便。苟临急以是为敀。庶其可也。难者曰。敌骑飙忽。瞬息突至。何能提挈老幼。安行以达。远水殆不救近火。凡此皆守之说也。而人各异见。将孰从而孰违。唯明于利害者而后。知所择矣。康兆以剑车。战元兵于鸭江上。所向披靡。虽其后也败。败由于酒。非车之咎。惜其制无传。当从古老问之。其后元以万骑送沈王。丽人伏兵江岸。邀而击之。乃无只轮匹蹄之得返。而见今江边地势。皆平夷无茂林大皋可以藏兵者。亦当求其地而按视。此则战之说也。而其不足徵如此。将何以取法。唯才略过众而后。能揆古而刱奇也。虽然。如盼子之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是岂善战善守之效哉。亦惟威信之素孚于邻耳。威非杀戮之谓。能守法律已。斯威立矣。信非约誓之谓。能尽诚接物。斯信著矣。苟如是。虽殊类异种。且怀吾之德。而争为之耳目。况我边民。其有不出死断亡而愉者乎。奚有于守。奚有于战哉。今年尹云仲。由弘文检讨。出为湾尹。云仲余所谓明于利害者也。寸(一作才)略过众者也。余故告之以此。且以威信勉其本焉。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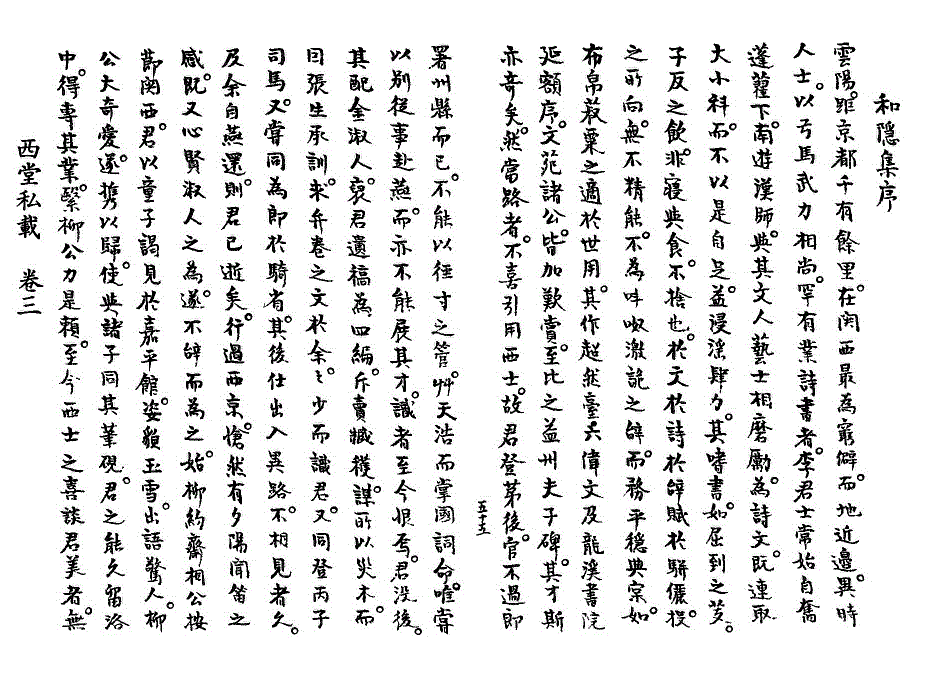 和隐集序
和隐集序云阳。距京都千有馀里。在关西最为穷僻。而地近边。异时人士。以弓马武力相尚。罕有业诗书者。李君士常始自奋蓬藋下。南游汉师。与其文人艺士相磨励。为诗文。既连取大小科。而不以是自足。益浸淫肆力。其嗜书。如屈到之芰。子反之饮。非寝与食。不舍也。于文于诗于辞赋于骈俪。投之所向。无不精能。不为叫呶激诡之辞。而务平稳典实。如布帛菽粟之适于世用。其作超然台,六伟文及龙溪书院延额序。文苑诸公。皆加叹赏。至比之益州夫子碑。其才斯亦奇矣。然当路者。不喜引用西士。故君登第后。官不过郎署州县而已。不能以径寸之管。草天浩而掌国词命。唯尝以别从事赴燕。而亦不能展其才。识者至今恨焉。君没后。其配金淑人。裒君遗稿为四编。斥卖臧穫。谋所以灾木。而因张生承训。求弁卷之文于余。余少而识君。又同登丙子司马。又尝同为郎于骑省。其后仕出入异路。不相见者久。及余自燕还。则君已逝矣。行过西京。怆然有夕阳闻笛之感。既又心贤淑人之为。遂不辞而为之。始柳约斋相公按节关西。君以童子谒见于嘉平馆。姿貌玉雪。出语惊人。柳公大奇爱。遂携以归。使与诸子同其笔砚。君之能久留洛中。得专其业。繄柳公力是赖。至今西士之喜谈君美者。无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1L 页
 不并称柳公云。君讳时恒。士常其字也。戊午四月。全义李某。序。
不并称柳公云。君讳时恒。士常其字也。戊午四月。全义李某。序。温陵志序
温陵志。志温陵事也。陵之墓而未陵也。虽妇孺之无所知。莫不冤悯痛伤。历数百年如一日。其既陵也。则又靡不欢欣抃跃。恨昔之未举。而庆今之快睹。若是者何哉。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间焉耳矣。夫天下之变故虽多端。其揆之也惟其义而已矣。所谓义者。即乎人心之所安。如斯而已矣。斯其为天理。而不以古今而有间焉者也。始之冤悯痛伤。历数百年如一日者。斯义也。今之欢欣抃跃。恨昔之未举。而庆今之快睹者。亦斯义也。人心之所安也。天理之不以古今而有间焉者也。规废规复。各有其人。其为臭为芳。亦人心之所同然。而非可强而使之者也。我 圣上所以即乎人心之所安。而揆之以义理。定古今不决之疑者。苟非 圣学之高明。又恶能及是。猗欤盛哉。温陵之考曰。左议政益昌府院君守勤。遇祸于举义之初。 上既奖其忠节。又赠以美谥。温陵在天之灵。于是乎庶无遗憾矣。益昌之八世孙后聃。悉取古今事迹凡系温陵事者。为是编。又以复陵时大小文字。附其后。其事该矣。间求余为弁卷之文。余尝撰益昌公谥状。备知其时事首末。故不辞而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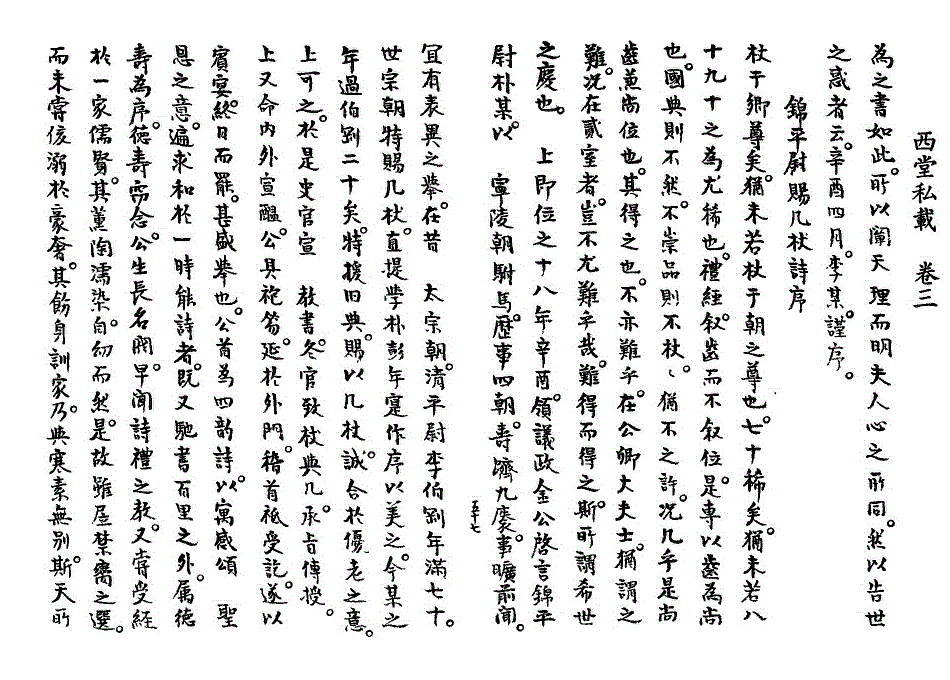 为之书如此。所以阐天理而明夫人心之所同。然以告世之惑者云。辛酉四月。李某。谨序。
为之书如此。所以阐天理而明夫人心之所同。然以告世之惑者云。辛酉四月。李某。谨序。锦平尉赐几杖诗序
杖于乡尊矣。犹未若杖于朝之尊也。七十稀矣。犹未若八十九十之为尤稀也。礼经。叙齿而不叙位。是专以齿为尚也。国典则不然。不崇品则不杖。杖犹不之许。况几乎是尚齿兼尚位也。其得之也。不亦难乎。在公卿大夫士。犹谓之难。况在贰室者。岂不尤难乎哉。难得而得之。斯所谓希世之庆也。 上即位之十八年辛酉。领议政金公启言锦平尉朴某。以 宁陵朝驸马。历事四朝。寿跻九帙。事旷前闻。宜有表异之举。在昔 太宗朝。清平尉李伯刚年满七十。世宗朝特赐几杖。直提学朴彭年寔作序以美之。今某之年过伯刚二十矣。特援旧典。赐以几杖。诚合于优老之意。上可之。于是史官宣 教书。冬官致杖与几。承旨传授。 上又命内外宣酝。公具袍笏。延于外门。稽首祗受讫。遂以宾宴。终日而罢。甚盛举也。公首为四韵诗。以寓感颂 圣恩之意。遍求和于一时能诗者。既又驰书百里之外。属德寿为序。德寿窃念。公生长名阀。早闻诗礼之教。又尝受经于一家儒贤。其薰陶濡染。自幼而然。是故虽㞐禁脔之选。而未尝侅溺于豪奢。其饬身训家。乃与寒素无别。斯天所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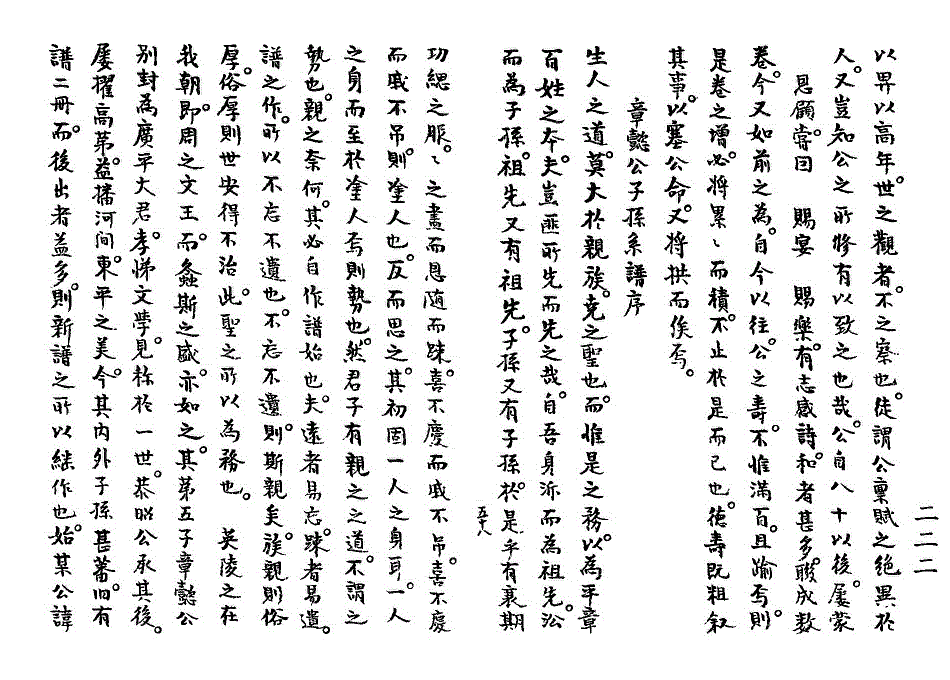 以畀以高年。世之观者。不之察也。徒谓公禀赋之绝异于人。又岂知公之所修有以致之也哉。公自八十以后。屡蒙 恩顾。尝因 赐宴 赐乐。有志感诗。和者甚多。联成数卷。今又如前之为。自今以往。公之寿。不惟满百。且踰焉。则是卷之增。必将累累而积。不止于是而已也。德寿既粗叙其事。以塞公命。又将拱而俟焉。
以畀以高年。世之观者。不之察也。徒谓公禀赋之绝异于人。又岂知公之所修有以致之也哉。公自八十以后。屡蒙 恩顾。尝因 赐宴 赐乐。有志感诗。和者甚多。联成数卷。今又如前之为。自今以往。公之寿。不惟满百。且踰焉。则是卷之增。必将累累而积。不止于是而已也。德寿既粗叙其事。以塞公命。又将拱而俟焉。章懿公子孙系谱序
生人之道。莫大于亲族。尧之圣也。而惟是之务。以为平章百姓之本。夫岂匪所先而先之哉。自吾身溯而为祖先。沿而为子孙。祖先又有祖先。子孙又有子孙。于是乎有衰期功缌之服。服之尽而恩随而疏。喜不庆而戚不吊。喜不庆而戚不吊。则涂人也。反而思之。其初固一人之身耳。一人之身而至于涂人焉则势也。然君子有亲之之道。不谓之势也。亲之奈何。其必自作谱始也。夫远者易忘。疏者易遗。谱之作。所以不忘不遗也。不忘不遗。则斯亲矣。族亲则俗厚。俗厚则世安得不治。此圣之所以为务也。 英陵之在我朝。即周之文王。而螽斯之盛。亦如之。其第五子章懿公别封为广平大君。孝悌文学。见称于一世。恭昭公承其后。屡擢高第。益播河间。东平之美。今其内外子孙甚蕃。旧有谱二册。而后出者益多。则新谱之所以继作也。始某公讳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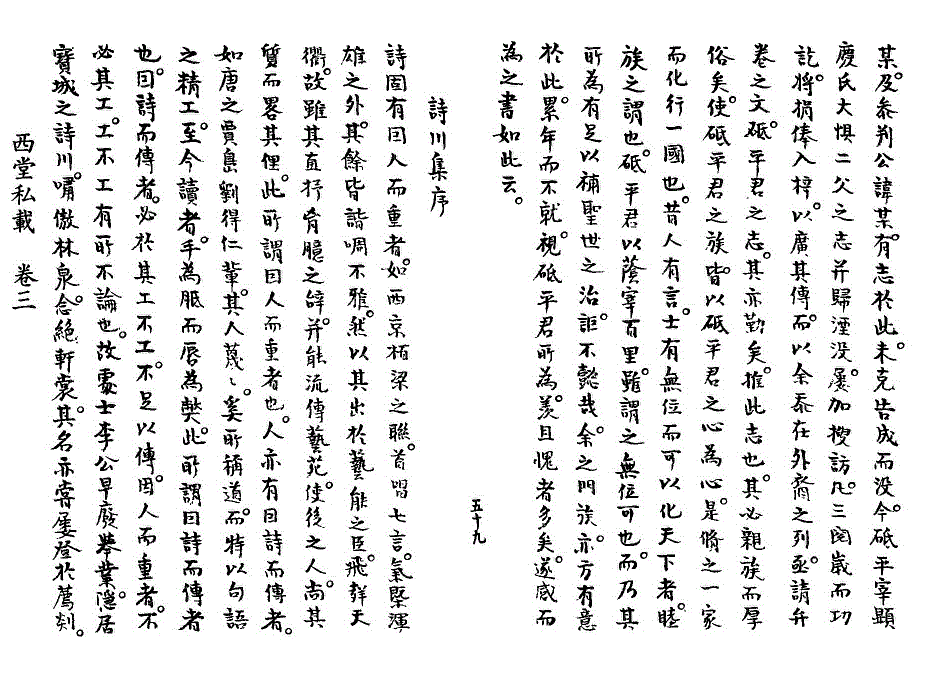 某。及参判公讳某。有志于此。未克告成而没。今砥平宰显庆氏大惧二父之志并归湮没。屡加搜访。凡三阅岁而功讫。将捐俸入梓。以广其传。而以余忝在外裔之列。亟请弁卷之文。砥平君之志。其亦勤矣。推此志也。其必亲族而厚俗矣。使砥平君之族。皆以砥平君之心为心。是脩之一家而化行一国也。昔人有言。士有无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之谓也。砥平君以荫宰百里。虽谓之无位可也。而乃其所为有足以补圣世之治。讵不懿哉。余之门族。亦方有意于此。累年而不就。视砥平君所为。羡且愧者多矣。遂感而为之书如此云。
某。及参判公讳某。有志于此。未克告成而没。今砥平宰显庆氏大惧二父之志并归湮没。屡加搜访。凡三阅岁而功讫。将捐俸入梓。以广其传。而以余忝在外裔之列。亟请弁卷之文。砥平君之志。其亦勤矣。推此志也。其必亲族而厚俗矣。使砥平君之族。皆以砥平君之心为心。是脩之一家而化行一国也。昔人有言。士有无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之谓也。砥平君以荫宰百里。虽谓之无位可也。而乃其所为有足以补圣世之治。讵不懿哉。余之门族。亦方有意于此。累年而不就。视砥平君所为。羡且愧者多矣。遂感而为之书如此云。诗川集序
诗固有因人而重者。如西京柏梁之联。首唱七言。气槩浑雄之外。其馀皆谐啁不雅。然以其出于艺能之臣。飞声天衢。故虽其直抒胸臆之辞。并能流传艺苑。使后之人。尚其质而略其俚。此所谓因人而重者也。人亦有因诗而传者。如唐之贾岛刘得仁辈。其人蔑蔑。奚所称道。而特以句语之精工。至今读者。手为胝而唇为弊。此所谓因诗而传者也。因诗而传者。必于其工不工。不足以传。因人而重者。不必其工。工不工有所不论也。故处士李公早废举业。隐居宝城之诗川。啸傲林泉。念绝轩裳。其名亦尝屡登于荐剡。
西堂私载卷之三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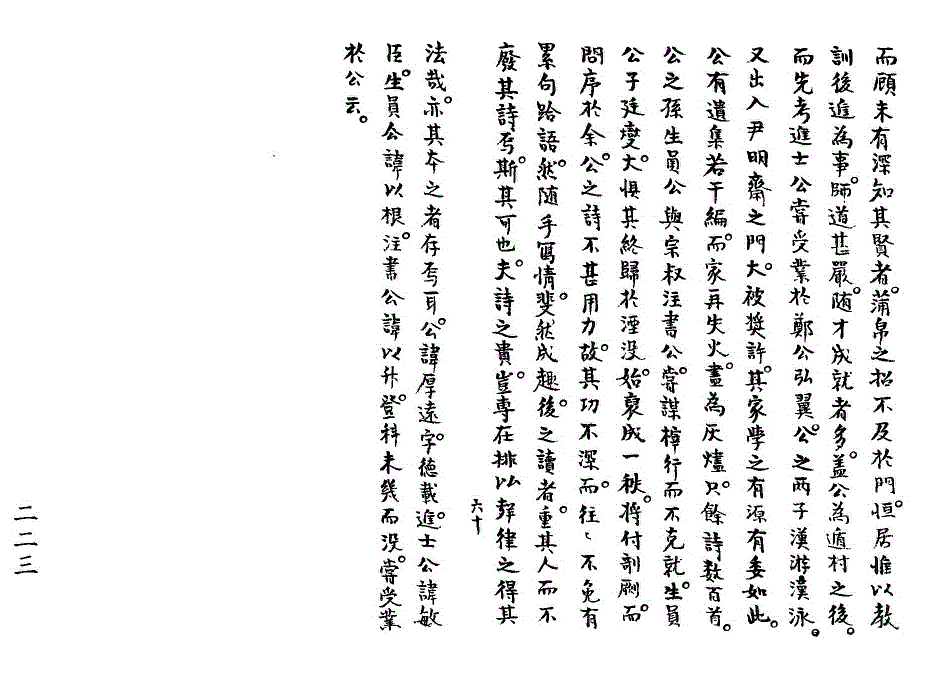 而顾未有深知其贤者。蒲帛之招不及于门。恒居惟以教训后进为事。师道甚严。随才成就者多。盖公为遁村之后。而先考进士公尝受业于郑公弘翼。公之两子汉游,汉泳。又出入尹明斋之门。大被奖许。其家学之有源有委如此。公有遗集若干编。而家再失火。尽为灰烬。只馀诗数百首。公之孙生员公与宗叔注书公。尝谋梓行而不克就。生员公子廷燮。大惧其终归于湮没。始裒成一秩。将付剞劂。而问序于余。公之诗不甚用力。故其功不深。而往往不免有累句跲语。然随手写情。斐然成趣。后之读者。重其人而不废其诗焉。斯其可也。夫诗之贵。岂专在排比声律之得其法哉。亦其本之者存焉耳。公讳厚远。字德载。进士公讳敏臣。生员公讳以根。注书公讳以升。登科未几而没。尝受业于公云。
而顾未有深知其贤者。蒲帛之招不及于门。恒居惟以教训后进为事。师道甚严。随才成就者多。盖公为遁村之后。而先考进士公尝受业于郑公弘翼。公之两子汉游,汉泳。又出入尹明斋之门。大被奖许。其家学之有源有委如此。公有遗集若干编。而家再失火。尽为灰烬。只馀诗数百首。公之孙生员公与宗叔注书公。尝谋梓行而不克就。生员公子廷燮。大惧其终归于湮没。始裒成一秩。将付剞劂。而问序于余。公之诗不甚用力。故其功不深。而往往不免有累句跲语。然随手写情。斐然成趣。后之读者。重其人而不废其诗焉。斯其可也。夫诗之贵。岂专在排比声律之得其法哉。亦其本之者存焉耳。公讳厚远。字德载。进士公讳敏臣。生员公讳以根。注书公讳以升。登科未几而没。尝受业于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