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x 页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序
拾遗录(文)○序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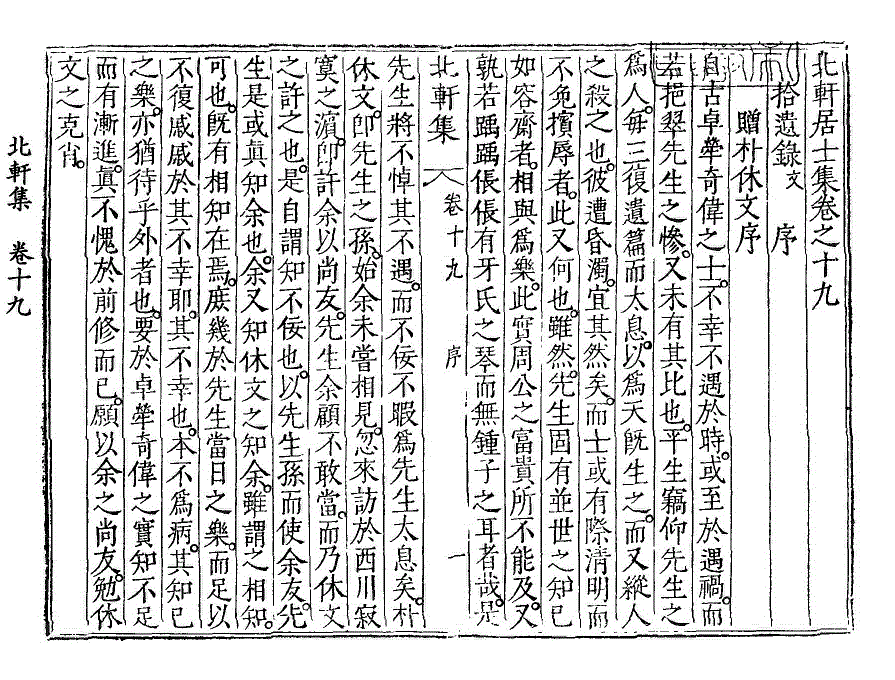 赠朴休文序
赠朴休文序自古卓荦奇伟之士。不幸不遇于时。或至于遇祸。而若挹翠先生之惨。又未有其比也。平生窃仰先生之为人。每三复遗篇而太息。以为天既生之。而又纵人之杀之也。彼遭昏浊。宜其然矣。而士或有际清明而不免摈辱者。此又何也。虽然。先生固有并世之知己如容斋者。相与为乐。此实周公之富贵所不能及。又孰若踽踽伥伥有牙氏之琴而无钟子之耳者哉。是先生将不悼其不遇。而不佞不暇为先生太息矣。朴休文。即先生之孙。始余未尝相见。忽来访于西川寂寞之滨。即许余以尚友。先生余顾不敢当。而乃休文之许之也。是自谓知不佞也。以先生孙而使余友。先生是或真知余也。余又知休文之知余。虽谓之相知。可也。既有相知在焉。庶几于先生当日之乐。而足以不复戚戚于其不幸耶。其不幸也。本不为病。其知己之乐。亦犹待乎外者也。要于卓荦奇伟之实知不足而有渐进。真不愧于前修而已。愿以余之尚友。勉休文之克肖。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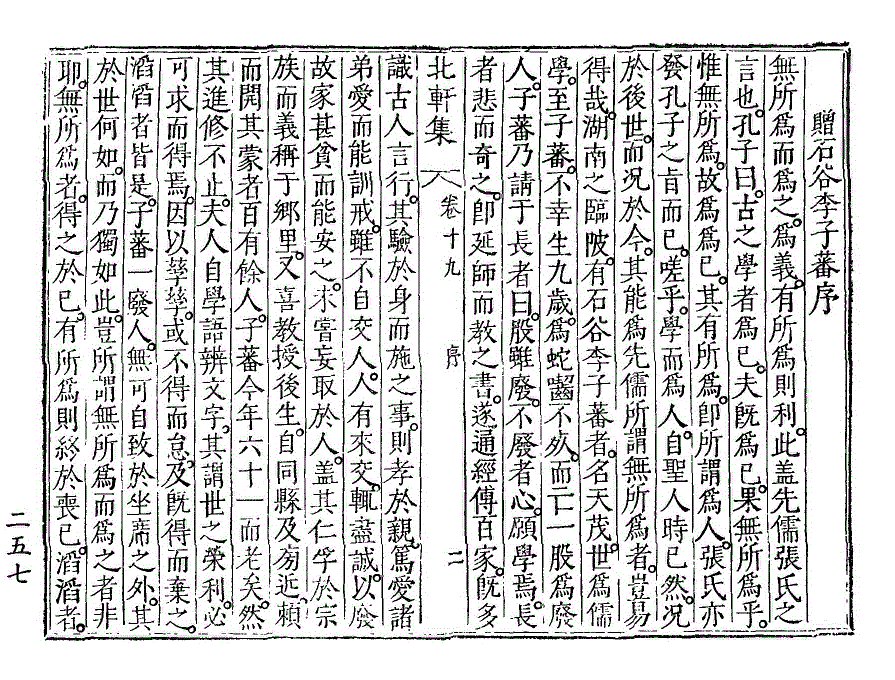 赠石谷李子蕃序
赠石谷李子蕃序无所为而为之。为义。有所为则利。此盖先儒张氏之言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夫既为己。果无所为乎。惟无所为。故为为己。其有所为。即所谓为人。张氏亦发孔子之旨而已。嗟乎。学而为人。自圣人时已然。况于后世。而况于今。其能为先儒所谓无所为者。岂易得哉。湖南之临陂。有石谷李子蕃者。名天茂。世为儒学。至子蕃。不幸生九岁。为蛇齧不死。而亡一股为废人。子蕃乃请于长者曰。股虽废。不废者心。愿学焉。长者悲而奇之。即延师而教之书。遂通经传百家。既多识古人言行。其验于身而施之事。则孝于亲。笃爱诸弟爱而能训戒。虽不自交人。人有来交。辄尽诚。以废故家甚贫而能安之。未尝妄取于人。盖其仁孚于宗族而义称于乡里。又喜教授后生。自同县及旁近。赖而开其蒙者百有馀人。子蕃今年六十一而老矣。然其进修不止。夫人自学语辨文字。其谓世之荣利。必可求而得焉。因以孳孳。或不得而怠。及既得而弃之。滔滔者皆是。子蕃一废人。无可自致于坐席之外。其于世何如。而乃独如此。岂所谓无所为而为之者非耶。无所为者。得之于己。有所为则终于丧己。滔滔者。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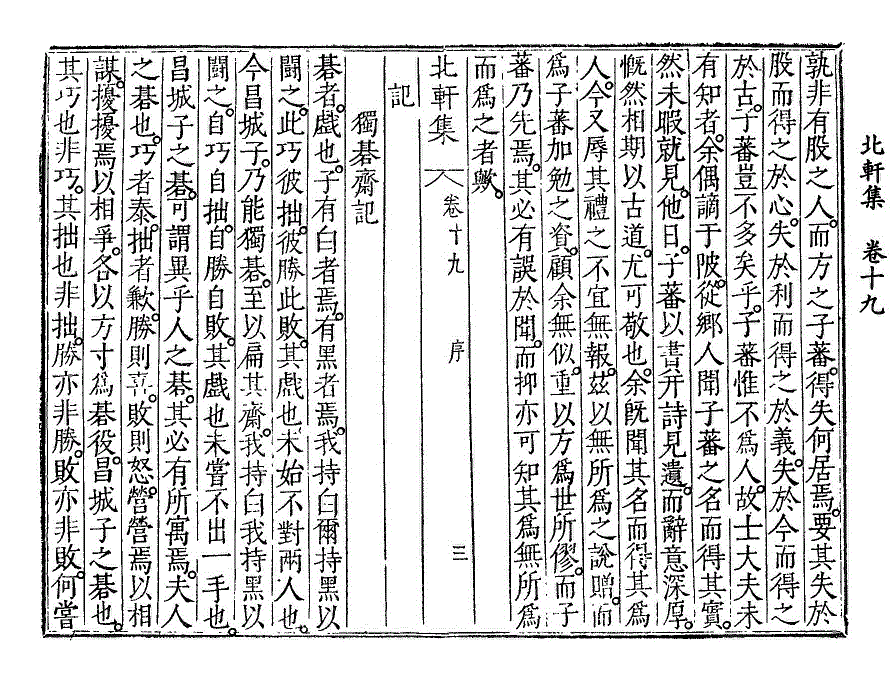 孰非有股之人。而方之子蕃。得失何居焉。要其失于股而得之于心。失于利而得之于义。失于今而得之于古。子蕃岂不多矣乎。子蕃惟不为人。故士大夫未有知者。余偶谪于陂。从乡人闻子蕃之名而得其实。然未暇就见。他日。子蕃以书并诗见遗。而辞意深厚。慨然相期以古道。尤可敬也。余既闻其名而得其为人。今又辱其礼之不宜无报。玆以无所为之说赠。而为子蕃加勉之资。顾余无似。重以方为世所僇。而子蕃乃先焉。其必有误于闻。而抑亦可知其为无所为而为之者欤。
孰非有股之人。而方之子蕃。得失何居焉。要其失于股而得之于心。失于利而得之于义。失于今而得之于古。子蕃岂不多矣乎。子蕃惟不为人。故士大夫未有知者。余偶谪于陂。从乡人闻子蕃之名而得其实。然未暇就见。他日。子蕃以书并诗见遗。而辞意深厚。慨然相期以古道。尤可敬也。余既闻其名而得其为人。今又辱其礼之不宜无报。玆以无所为之说赠。而为子蕃加勉之资。顾余无似。重以方为世所僇。而子蕃乃先焉。其必有误于闻。而抑亦可知其为无所为而为之者欤。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记
独棋斋记
棋者。戏也。子有白者焉。有黑者焉。我持白尔持黑以斗之。此巧彼拙。彼胜此败。其戏也未始不对两人也。今昌城子。乃能独棋。至以扁其斋。我持白我持黑以斗之。自巧自拙。自胜自败。其戏也未尝不出一手也。昌城子之棋。可谓异乎人之棋。其必有所寓焉。夫人之棋也。巧者泰。拙者歉。胜则喜。败则怒。营营焉以相谋。扰扰焉以相争。各以方寸为棋役。昌城子之棋也。其巧也非巧。其拙也非拙。胜亦非胜。败亦非败。何尝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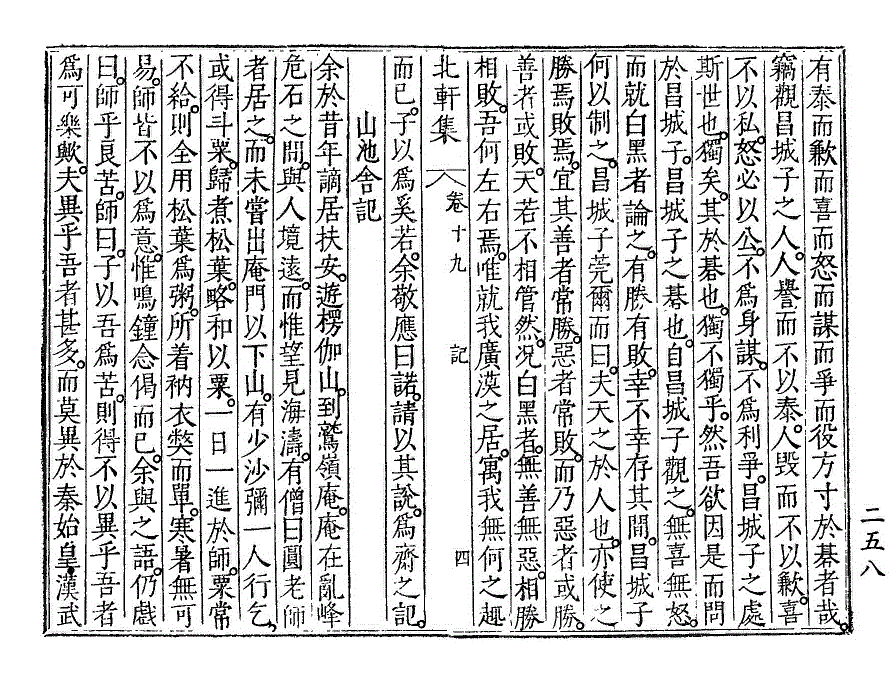 有泰而歉而喜而怒而谋而争而役方寸于棋者哉。窃观昌城子之人。人誉而不以泰。人毁而不以歉。喜不以私。怒必以公。不为身谋。不为利争。昌城子之处斯世也。独矣。其于棋也。独不独乎。然吾欲因是而问于昌城子。昌城子之棋也。自昌城子观之。无喜无怒。而就白黑者论之。有胜有败。幸不幸存其间。昌城子何以制之。昌城子莞尔而曰。夫天之于人也。亦使之胜焉败焉。宜其善者常胜。恶者常败。而乃恶者或胜。善者或败。天若不相管然。况白黑者。无善无恶。相胜相败。吾何左右焉。唯就我广漠之居。寓我无何之趣而已。子以为奚若。余敬应曰诺。请以其说。为斋之记。
有泰而歉而喜而怒而谋而争而役方寸于棋者哉。窃观昌城子之人。人誉而不以泰。人毁而不以歉。喜不以私。怒必以公。不为身谋。不为利争。昌城子之处斯世也。独矣。其于棋也。独不独乎。然吾欲因是而问于昌城子。昌城子之棋也。自昌城子观之。无喜无怒。而就白黑者论之。有胜有败。幸不幸存其间。昌城子何以制之。昌城子莞尔而曰。夫天之于人也。亦使之胜焉败焉。宜其善者常胜。恶者常败。而乃恶者或胜。善者或败。天若不相管然。况白黑者。无善无恶。相胜相败。吾何左右焉。唯就我广漠之居。寓我无何之趣而已。子以为奚若。余敬应曰诺。请以其说。为斋之记。山池舍记
余于昔年谪居扶安。游楞伽山。到鹫岭庵。庵在乱峰危石之间。与人境远。而惟望见海涛。有僧曰圆老师者居之。而未尝出庵门以下山。有少沙弥一人行乞。或得斗粟。归煮松叶。略和以粟。一日一进于师。粟常不给。则全用松叶为粥。所着衲衣弊而单。寒暑无可易。师皆不以为意。惟鸣钟念偈而已。余与之语。仍戏曰。师乎良苦。师曰。子以吾为苦。则得不以异乎吾者为可乐欤。夫异乎吾者甚多。而莫异于秦始皇,汉武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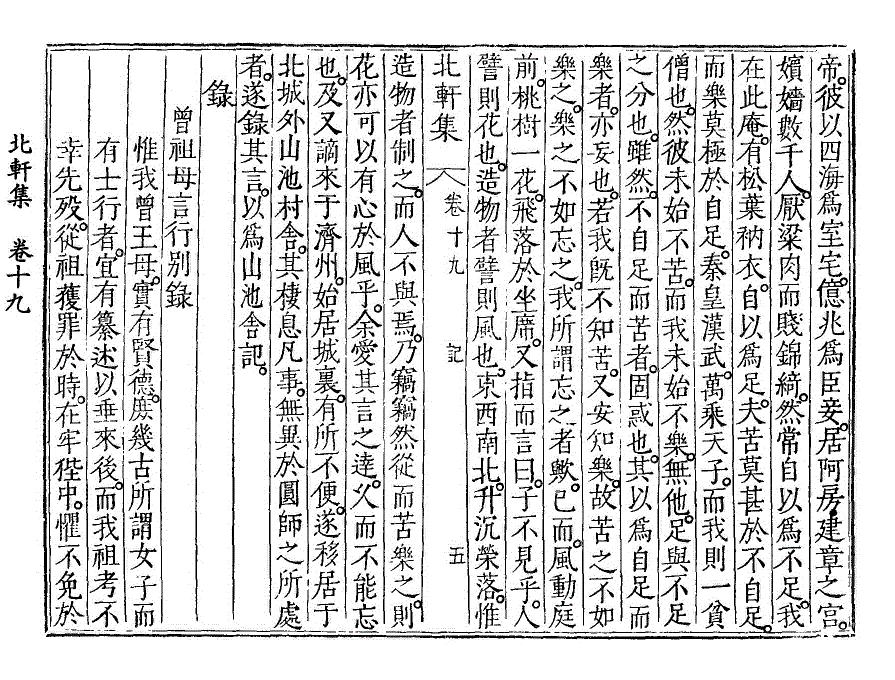 帝。彼以四海为室宅。亿兆为臣妾。居阿房,建章之宫。嫔嫱数千人。厌粱肉而贱锦绮。然常自以为不足。我在此庵。有松叶衲衣。自以为足。夫苦莫甚于不自足。而乐莫极于自足。秦皇汉武。万乘天子。而我则一贫僧也。然彼未始不苦。而我未始不乐。无他。足与不足之分也。虽然。不自足而苦者。固惑也。其以为自足而乐者。亦妄也。若我既不知苦。又安知乐。故苦之不如乐之。乐之不如忘之。我所谓忘之者欤。已而。风动庭前。桃树一花。飞落于坐席。又指而言曰。子不见乎。人譬则花也。造物者譬则风也。东西南北。升沉荣落。惟造物者制之。而人不与焉。乃窃窃然从而苦乐之。则花亦可以有心于风乎。余爱其言之达。久而不能忘也。及又谪来于济州。始居城里。有所不便。遂移居于北城外山池村舍。其栖息凡事。无异于圆师之所处者。遂录其言。以为山池舍记。
帝。彼以四海为室宅。亿兆为臣妾。居阿房,建章之宫。嫔嫱数千人。厌粱肉而贱锦绮。然常自以为不足。我在此庵。有松叶衲衣。自以为足。夫苦莫甚于不自足。而乐莫极于自足。秦皇汉武。万乘天子。而我则一贫僧也。然彼未始不苦。而我未始不乐。无他。足与不足之分也。虽然。不自足而苦者。固惑也。其以为自足而乐者。亦妄也。若我既不知苦。又安知乐。故苦之不如乐之。乐之不如忘之。我所谓忘之者欤。已而。风动庭前。桃树一花。飞落于坐席。又指而言曰。子不见乎。人譬则花也。造物者譬则风也。东西南北。升沉荣落。惟造物者制之。而人不与焉。乃窃窃然从而苦乐之。则花亦可以有心于风乎。余爱其言之达。久而不能忘也。及又谪来于济州。始居城里。有所不便。遂移居于北城外山池村舍。其栖息凡事。无异于圆师之所处者。遂录其言。以为山池舍记。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录
曾祖母言行别录
惟我曾王母。实有贤德。庶几古所谓女子而有士行者。宜有纂述以垂来后。而我祖考不幸先殁。从祖获罪于时。在牢狴中。惧不免于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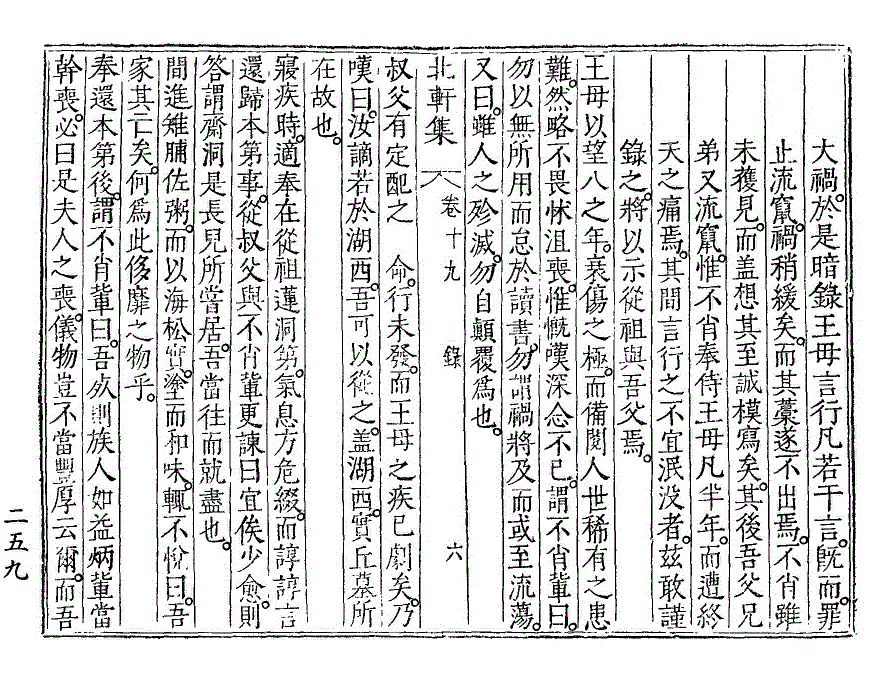 大祸。于是暗录王母言行凡若干言。既而。罪止流窜。祸稍缓矣。而其藁遂不出焉。不肖虽未获见。而盖想其至诚模写矣。其后吾父兄弟又流窜。惟不肖奉侍王母凡半年。而遭终天之痛焉。其间言行之不宜泯没者。玆敢谨录之。将以示从祖与吾父焉。
大祸。于是暗录王母言行凡若干言。既而。罪止流窜。祸稍缓矣。而其藁遂不出焉。不肖虽未获见。而盖想其至诚模写矣。其后吾父兄弟又流窜。惟不肖奉侍王母凡半年。而遭终天之痛焉。其间言行之不宜泯没者。玆敢谨录之。将以示从祖与吾父焉。王母以望八之年。衰伤之极。而备阅人世稀有之患难。然略不畏怵沮丧。惟慨叹深念不已。谓不肖辈曰。勿以无所用而怠于读书。勿谓祸将及而或至流荡。又曰。虽人之殄灭。勿自颠覆为也。
叔父有定配之 命。行未发。而王母之疾已剧矣。乃叹曰。汝谪若于湖西。吾可以从之。盖湖西。实丘墓所在故也。
寝疾时。适奉在从祖莲洞第。气息方危缀。而谆谆言还归本第事。从叔父与不肖辈更谏曰宜俟少愈。则答谓斋洞是长儿所尝居。吾当往而就尽也。
间进雉脯佐粥。而以海松实。涂而和味。辄不悦曰。吾家其亡矣。何为此侈靡之物乎。
奉还本第后。谓不肖辈曰。吾死则族人如益炳辈当干丧。必曰是夫人之丧。仪物岂不当丰厚云尔。而吾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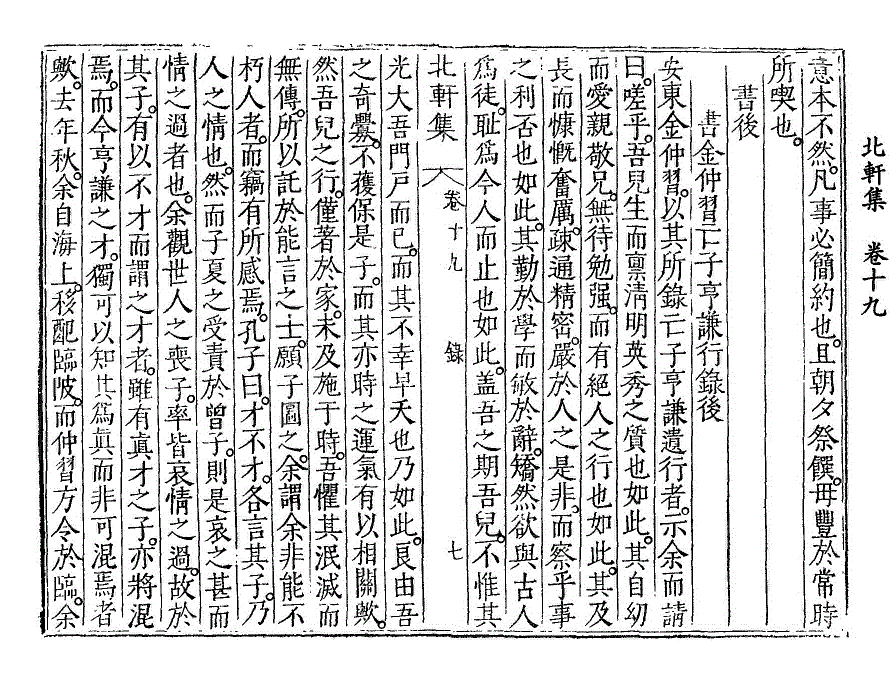 意本不然。凡事必简约也。且朝夕祭馔。毋丰于常时所吃也。
意本不然。凡事必简约也。且朝夕祭馔。毋丰于常时所吃也。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书后
书金仲习亡子亨谦行录后
安东金仲习。以其所录亡子亨谦遗行者。示余而请曰。嗟乎。吾儿生而禀清明英秀之质也如此。其自幼而爱亲敬兄。无待勉强。而有绝人之行也如此。其及长而慷慨奋厉。疏通精密。严于人之是非。而察乎事之利否也如此。其勤于学而敏于辞。矫然欲与古人为徒。耻为今人而止也如此。盖吾之期吾儿。不惟其光大吾门户而已。而其不幸早夭也乃如此。良由吾之奇衅。不获保是子。而其亦时之运气有以相关欤。然吾儿之行。仅著于家。未及施于时。吾惧其泯灭而无传。所以托于能言之士。愿子图之。余谓余非能不朽人者。而窃有所感焉。孔子曰。才不才。各言其子。乃人之情也。然而子夏之受责于曾子。则是哀之甚而情之过者也。余观世人之丧子。率皆哀情之过。故于其子。有以不才而谓之才者。虽有真才之子。亦将混焉。而今亨谦之才。独可以知其为真而非可混焉者欤。去年秋。余自海上。移配临陂。而仲习方令于临。余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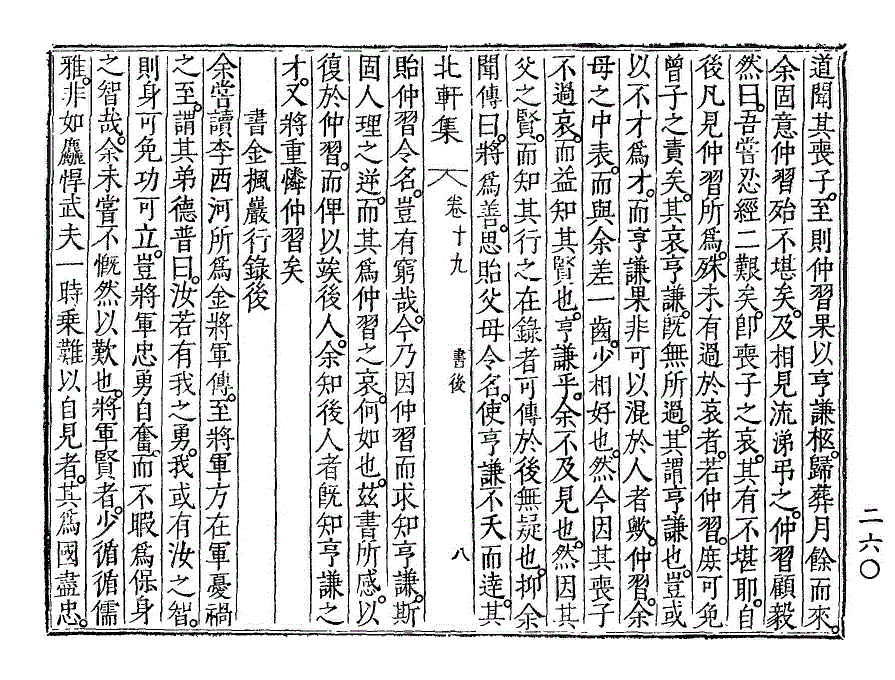 道闻其丧子。至则仲习果以亨谦柩。归葬月馀而来。余固意仲习殆不堪矣。及相见流涕吊之。仲习顾毅然曰。吾尝忍经二艰矣。即丧子之哀。其有不堪耶。自后凡见仲习所为。殊未有过于哀者。若仲习。庶可免曾子之责矣。其哀亨谦。既无所过。其谓亨谦也。岂或以不才为才。而亨谦果非可以混于人者欤。仲习。余母之中表。而与余差一齿。少相好也。然今因其丧子不过哀。而益知其贤也。亨谦乎。余不及见也。然因其父之贤。而知其行之在录者可传于后无疑也。抑余闻传曰。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使亨谦不夭而达。其贻仲习令名。岂有穷哉。今乃因仲习而求知亨谦。斯固人理之逆。而其为仲习之哀。何如也。玆书所感。以复于仲习。而俾以俟后人。余知后人者既知亨谦之才。又将重怜仲习矣。
道闻其丧子。至则仲习果以亨谦柩。归葬月馀而来。余固意仲习殆不堪矣。及相见流涕吊之。仲习顾毅然曰。吾尝忍经二艰矣。即丧子之哀。其有不堪耶。自后凡见仲习所为。殊未有过于哀者。若仲习。庶可免曾子之责矣。其哀亨谦。既无所过。其谓亨谦也。岂或以不才为才。而亨谦果非可以混于人者欤。仲习。余母之中表。而与余差一齿。少相好也。然今因其丧子不过哀。而益知其贤也。亨谦乎。余不及见也。然因其父之贤。而知其行之在录者可传于后无疑也。抑余闻传曰。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使亨谦不夭而达。其贻仲习令名。岂有穷哉。今乃因仲习而求知亨谦。斯固人理之逆。而其为仲习之哀。何如也。玆书所感。以复于仲习。而俾以俟后人。余知后人者既知亨谦之才。又将重怜仲习矣。书金枫岩行录后
余尝读李西河所为金将军传。至将军方在军忧祸之至。谓其弟德普曰。汝若有我之勇。我或有汝之智。则身可免功可立。岂将军忠勇自奋。而不暇为保身之智哉。余未尝不慨然以叹也。将军贤者。少循循儒雅。非如粗悍武夫一时乘难以自见者。其为国尽忠。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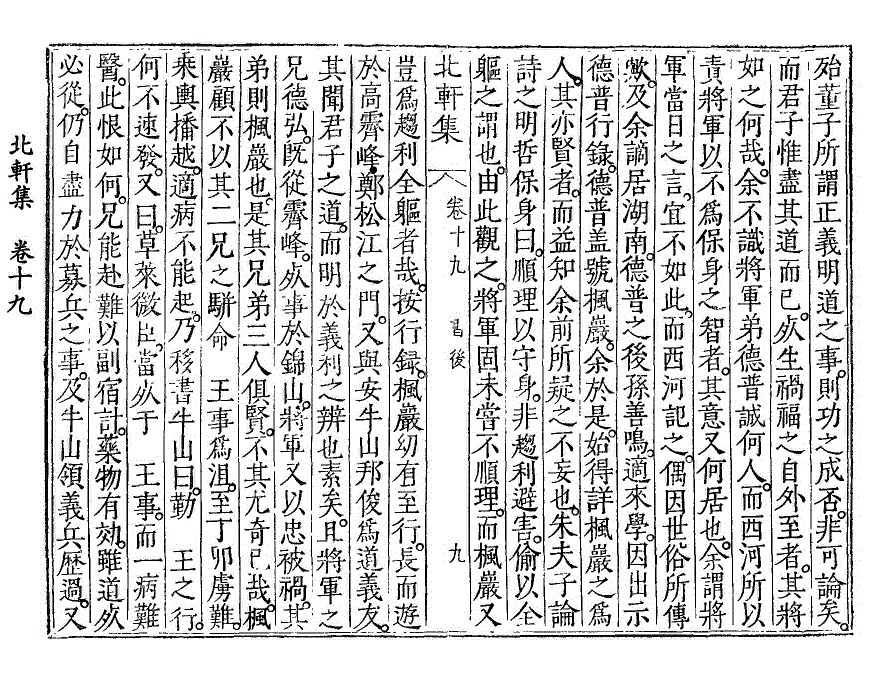 殆董子所谓正义明道之事。则功之成否。非可论矣。而君子惟尽其道而已。死生祸福之自外至者。其将如之何哉。余不识将军弟德普诚何人。而西河所以责将军以不为保身之智者。其意又何居也。余谓将军当日之言。宜不如此。而西河记之。偶因世俗所传欤。及余谪居湖南。德普之后孙善鸣。适来学。因出示德普行录。德普盖号枫岩。余于是。始得详枫岩之为人。其亦贤者。而益知余前所疑之不妄也。朱夫子论诗之明哲保身曰。顺理以守身。非趋利避害。偷以全躯之谓也。由此观之。将军固未尝不顺理。而枫岩又岂为趋利全躯者哉。按行录。枫岩幼有至行。长而游于高霁峰,郑松江之门。又与安牛山邦俊为道义友。其闻君子之道。而明于义利之辨也素矣。且将军之兄德弘。既从霁峰。死事于锦山。将军又以忠被祸。其弟则枫岩也。是其兄弟三人俱贤。不其尤奇已哉。枫岩顾不以其二兄之骈命 王事为沮。至丁卯虏难。乘舆播越。适病不能起。乃移书牛山曰。勤 王之行。何不速发。又曰。草莱微臣。当死于 王事。而一病难医。此恨如何。兄能赴难以副宿计。药物有效。虽道死必从。仍自尽力于募兵之事。及牛山领义兵历过。又
殆董子所谓正义明道之事。则功之成否。非可论矣。而君子惟尽其道而已。死生祸福之自外至者。其将如之何哉。余不识将军弟德普诚何人。而西河所以责将军以不为保身之智者。其意又何居也。余谓将军当日之言。宜不如此。而西河记之。偶因世俗所传欤。及余谪居湖南。德普之后孙善鸣。适来学。因出示德普行录。德普盖号枫岩。余于是。始得详枫岩之为人。其亦贤者。而益知余前所疑之不妄也。朱夫子论诗之明哲保身曰。顺理以守身。非趋利避害。偷以全躯之谓也。由此观之。将军固未尝不顺理。而枫岩又岂为趋利全躯者哉。按行录。枫岩幼有至行。长而游于高霁峰,郑松江之门。又与安牛山邦俊为道义友。其闻君子之道。而明于义利之辨也素矣。且将军之兄德弘。既从霁峰。死事于锦山。将军又以忠被祸。其弟则枫岩也。是其兄弟三人俱贤。不其尤奇已哉。枫岩顾不以其二兄之骈命 王事为沮。至丁卯虏难。乘舆播越。适病不能起。乃移书牛山曰。勤 王之行。何不速发。又曰。草莱微臣。当死于 王事。而一病难医。此恨如何。兄能赴难以副宿计。药物有效。虽道死必从。仍自尽力于募兵之事。及牛山领义兵历过。又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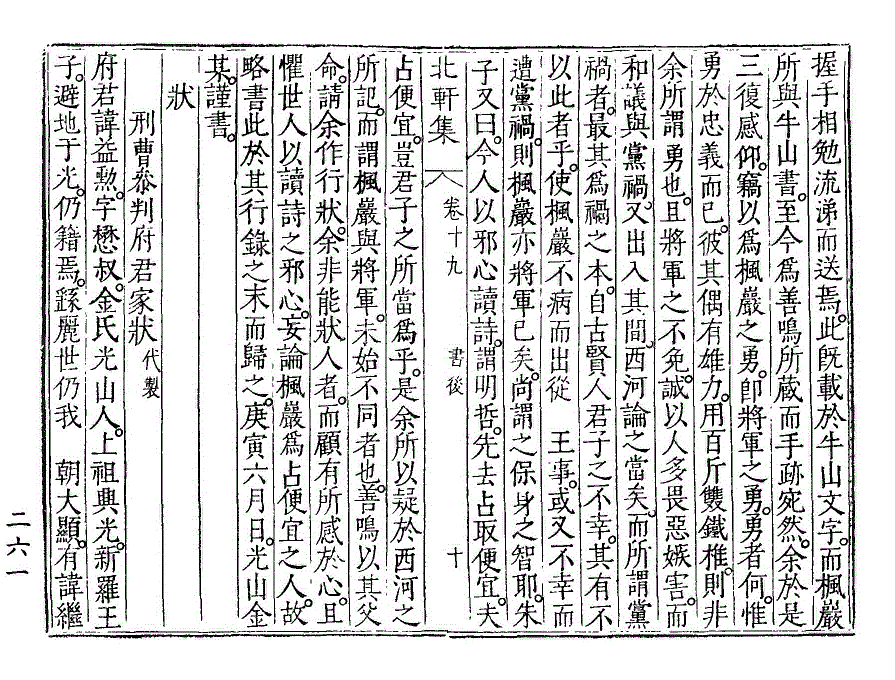 握手相勉流涕而送焉。此既载于牛山文字。而枫岩所与牛山书。至今为善鸣所藏而手迹宛然。余于是三复感仰。窃以为枫岩之勇。即将军之勇。勇者何。惟勇于忠义而已。彼其偶有雄力。用百斤双铁椎。则非余所谓勇也。且将军之不免。诚以人多畏恶嫉害。而和议与党祸。又出入其间。西河论之当矣。而所谓党祸者。最其为祸之本。自古贤人君子之不幸。其有不以此者乎。使枫岩不病而出从 王事。或又不幸而遭党祸。则枫岩亦将军已矣。尚谓之保身之智耶。朱子又曰。今人以邪心读诗。谓明哲。先去占取便宜。夫占便宜。岂君子之所当为乎。是余所以疑于西河之所记。而谓枫岩与将军。未始不同者也。善鸣以其父命。请余作行状。余非能状人者。而顾有所感于心。且惧世人以读诗之邪心。妄论枫岩为占便宜之人。故略书此于其行录之末而归之。庚寅六月日。光山金某。谨书。
握手相勉流涕而送焉。此既载于牛山文字。而枫岩所与牛山书。至今为善鸣所藏而手迹宛然。余于是三复感仰。窃以为枫岩之勇。即将军之勇。勇者何。惟勇于忠义而已。彼其偶有雄力。用百斤双铁椎。则非余所谓勇也。且将军之不免。诚以人多畏恶嫉害。而和议与党祸。又出入其间。西河论之当矣。而所谓党祸者。最其为祸之本。自古贤人君子之不幸。其有不以此者乎。使枫岩不病而出从 王事。或又不幸而遭党祸。则枫岩亦将军已矣。尚谓之保身之智耶。朱子又曰。今人以邪心读诗。谓明哲。先去占取便宜。夫占便宜。岂君子之所当为乎。是余所以疑于西河之所记。而谓枫岩与将军。未始不同者也。善鸣以其父命。请余作行状。余非能状人者。而顾有所感于心。且惧世人以读诗之邪心。妄论枫岩为占便宜之人。故略书此于其行录之末而归之。庚寅六月日。光山金某。谨书。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状
刑曹参判府君家状(代制)
府君讳益勋。字懋叔。金氏光山人。上祖兴光。新罗王子。避地于光。仍籍焉。繇丽世仍我 朝大显。有讳继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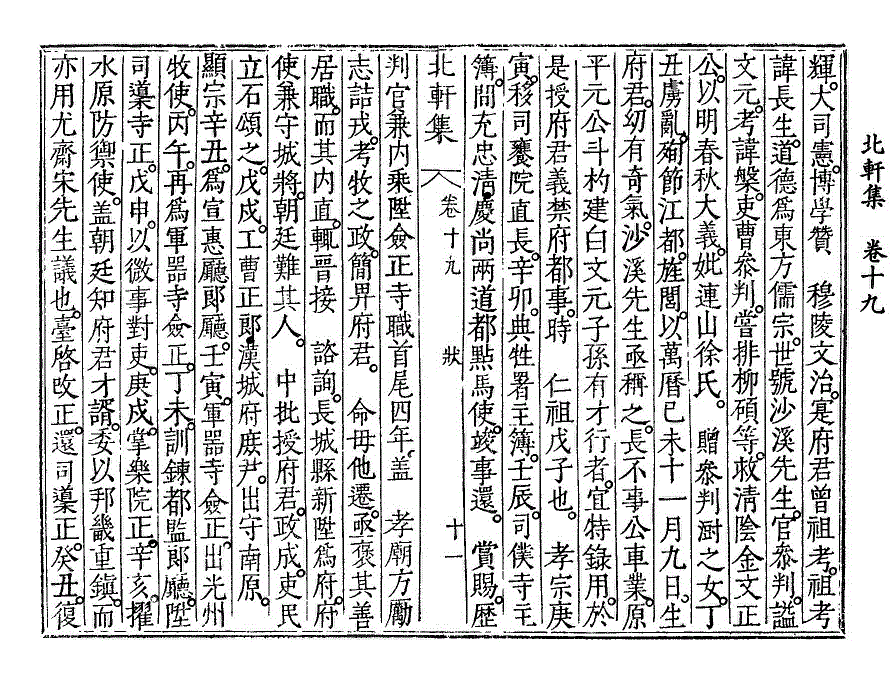 辉。大司宪。博学赞 穆陵文治。寔府君曾祖考。祖考讳长生。道德为东方儒宗。世号沙溪先生。官参判。谥文元。考讳槃。吏曹参判。尝排柳硕等。救清阴金文正公。以明春秋大义。妣连山徐氏。 赠参判澍之女。丁丑虏乱。殉节江都。旌闾。以万历己未十一月九日。生府君。幼有奇气。沙溪先生亟称之。长不事公车业。原平元公斗杓建白文元子孙有才行者。宜特录用。于是授府君义禁府都事。时 仁祖戊子也。 孝宗庚寅。移司饔院直长。辛卯。典牲署主簿。壬辰。司仆寺主簿。间充忠清,庆尚两道都点马使。竣事还。 赏赐。历判官兼内乘升佥正寺职首尾四年。盖 孝庙方励志诘戎。考牧之政。简畀府君。 命毋他迁。亟褒其善居职。而其内直。辄晋接 咨询。长城县新升为府。府使兼守城将。朝廷难其人。 中批授府君。政成。吏民立石颂之。戊戌。工曹正郎,汉城府庶尹。出守南原。 显宗辛丑。为宣惠厅郎厅。壬寅。军器寺佥正。出光州牧使。丙午。再为军器寺佥正。丁未。训鍊都监郎厅。升司䆃寺正。戊申。以微事对吏。庚戌。掌乐院正。辛亥。擢水原防御使。盖朝廷知府君才谞。委以邦畿重镇。而亦用尤斋宋先生议也。台启改正。还司䆃正。癸丑。复
辉。大司宪。博学赞 穆陵文治。寔府君曾祖考。祖考讳长生。道德为东方儒宗。世号沙溪先生。官参判。谥文元。考讳槃。吏曹参判。尝排柳硕等。救清阴金文正公。以明春秋大义。妣连山徐氏。 赠参判澍之女。丁丑虏乱。殉节江都。旌闾。以万历己未十一月九日。生府君。幼有奇气。沙溪先生亟称之。长不事公车业。原平元公斗杓建白文元子孙有才行者。宜特录用。于是授府君义禁府都事。时 仁祖戊子也。 孝宗庚寅。移司饔院直长。辛卯。典牲署主簿。壬辰。司仆寺主簿。间充忠清,庆尚两道都点马使。竣事还。 赏赐。历判官兼内乘升佥正寺职首尾四年。盖 孝庙方励志诘戎。考牧之政。简畀府君。 命毋他迁。亟褒其善居职。而其内直。辄晋接 咨询。长城县新升为府。府使兼守城将。朝廷难其人。 中批授府君。政成。吏民立石颂之。戊戌。工曹正郎,汉城府庶尹。出守南原。 显宗辛丑。为宣惠厅郎厅。壬寅。军器寺佥正。出光州牧使。丙午。再为军器寺佥正。丁未。训鍊都监郎厅。升司䆃寺正。戊申。以微事对吏。庚戌。掌乐院正。辛亥。擢水原防御使。盖朝廷知府君才谞。委以邦畿重镇。而亦用尤斋宋先生议也。台启改正。还司䆃正。癸丑。复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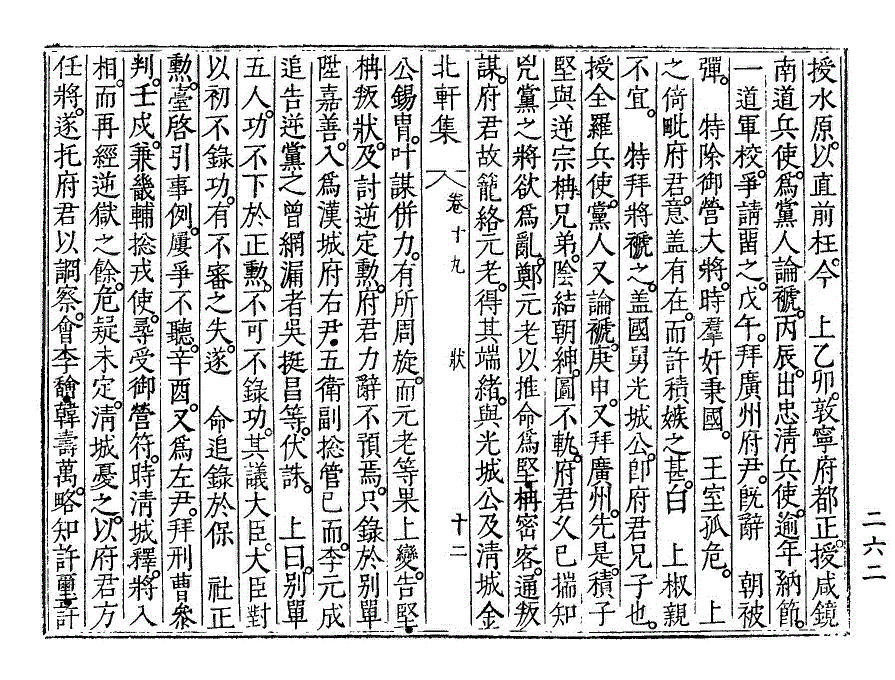 授水原。以直前枉。今 上乙卯。敦宁府都正。授咸镜南道兵使。为党人论褫。丙辰。出忠清兵使。逾年纳节。一道军校。争请留之。戊午。拜广州府尹。既辞 朝被弹。 特除御营大将。时群奸秉国。 王室孤危。 上之倚毗府君。意盖有在。而许积嫉之甚。白 上椒亲不宜。 特拜将褫之。盖国舅光城公。即府君兄子也。授全罗兵使。党人又论褫。庚申。又拜广州。先是。积子坚与逆宗楠兄弟。阴结朝绅。图不轨。府君久已揣知凶党之将欲为乱。郑元老以推命为坚,楠密客。通叛谋。府君故笼络元老。得其端绪。与光城公及清城金公锡胄。叶谋并力。有所周旋。而元老等果上变。告坚,楠叛状。及讨逆定勋。府君力辞不预焉。只录于别单升嘉善。入为汉城府右尹,五卫副总管已而。李元成追告逆党之曾网漏者吴挺昌等。伏诛。 上曰。别单五人。功不下于正勋。不可不录功。其议大臣。大臣对以初不录功。有不审之失。遂 命追录于保 社正勋。台启引事例。屡争不听。辛酉。又为左尹。拜刑曹参判。壬戌。兼畿辅总戎使。寻受御营符。时清城释。将入相。而再经逆狱之馀。危疑未定。清城忧之。以府君方任将。遂托府君以诇察。会李■(香会),韩寿万。略知许玺,许
授水原。以直前枉。今 上乙卯。敦宁府都正。授咸镜南道兵使。为党人论褫。丙辰。出忠清兵使。逾年纳节。一道军校。争请留之。戊午。拜广州府尹。既辞 朝被弹。 特除御营大将。时群奸秉国。 王室孤危。 上之倚毗府君。意盖有在。而许积嫉之甚。白 上椒亲不宜。 特拜将褫之。盖国舅光城公。即府君兄子也。授全罗兵使。党人又论褫。庚申。又拜广州。先是。积子坚与逆宗楠兄弟。阴结朝绅。图不轨。府君久已揣知凶党之将欲为乱。郑元老以推命为坚,楠密客。通叛谋。府君故笼络元老。得其端绪。与光城公及清城金公锡胄。叶谋并力。有所周旋。而元老等果上变。告坚,楠叛状。及讨逆定勋。府君力辞不预焉。只录于别单升嘉善。入为汉城府右尹,五卫副总管已而。李元成追告逆党之曾网漏者吴挺昌等。伏诛。 上曰。别单五人。功不下于正勋。不可不录功。其议大臣。大臣对以初不录功。有不审之失。遂 命追录于保 社正勋。台启引事例。屡争不听。辛酉。又为左尹。拜刑曹参判。壬戌。兼畿辅总戎使。寻受御营符。时清城释。将入相。而再经逆狱之馀。危疑未定。清城忧之。以府君方任将。遂托府君以诇察。会李■(香会),韩寿万。略知许玺,许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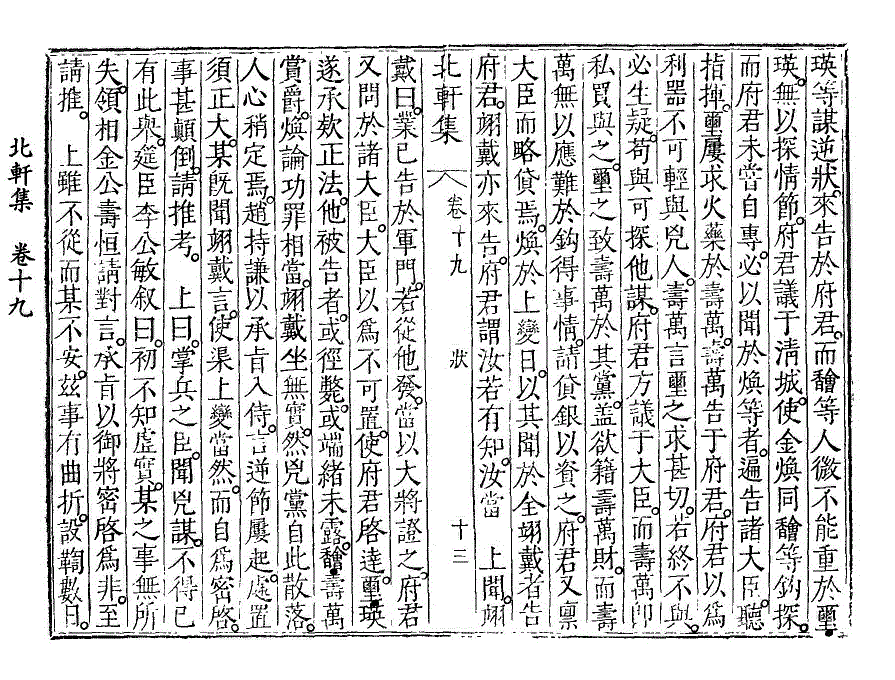 瑛等谋逆状。来告于府君。而■(香会)等人微不能重于玺,瑛。无以探情节。府君议于清城。使金焕同■(香会)等钩探。而府君未尝自专。必以闻于焕等者。遍告诸大臣。听指挥。玺屡求火药于寿万。寿万告于府君。府君以为利器不可轻与凶人。寿万言玺之求甚切。若终不与。必生疑。苟与可探他谋。府君方议于大臣。而寿万即私买与之。玺之致寿万于其党。盖欲籍寿万财。而寿万无以应难于钩得事情。请贷银以资之。府君又禀大臣而略贷焉。焕于上变日。以其闻于全翊戴者告府君。翊戴亦来告。府君谓汝若有知。汝当 上闻。翊戴曰。业已告于军门。若从他发。当以大将證之。府君又问于诸大臣。大臣以为不可置。使府君启达。玺,瑛遂承款正法。他被告者。或径毙。或端绪未露。■(香会),寿万赏爵。焕论功罪相当。翊戴坐无实。然凶党自此散落。人心稍定焉。赵持谦以承旨入侍。言逆节屡起。处置须正大。某既闻翊戴言。使渠上变当然。而自为密启。事甚颠倒。请推考。 上曰。掌兵之臣。闻凶谋。不得已有此举。筵臣李公敏叙曰。初不知虚实。某之事无所失。领相金公寿恒请对言。承旨以御将密启为非。至请推。 上虽不从而某不安。玆事有曲折。设鞫数日。
瑛等谋逆状。来告于府君。而■(香会)等人微不能重于玺,瑛。无以探情节。府君议于清城。使金焕同■(香会)等钩探。而府君未尝自专。必以闻于焕等者。遍告诸大臣。听指挥。玺屡求火药于寿万。寿万告于府君。府君以为利器不可轻与凶人。寿万言玺之求甚切。若终不与。必生疑。苟与可探他谋。府君方议于大臣。而寿万即私买与之。玺之致寿万于其党。盖欲籍寿万财。而寿万无以应难于钩得事情。请贷银以资之。府君又禀大臣而略贷焉。焕于上变日。以其闻于全翊戴者告府君。翊戴亦来告。府君谓汝若有知。汝当 上闻。翊戴曰。业已告于军门。若从他发。当以大将證之。府君又问于诸大臣。大臣以为不可置。使府君启达。玺,瑛遂承款正法。他被告者。或径毙。或端绪未露。■(香会),寿万赏爵。焕论功罪相当。翊戴坐无实。然凶党自此散落。人心稍定焉。赵持谦以承旨入侍。言逆节屡起。处置须正大。某既闻翊戴言。使渠上变当然。而自为密启。事甚颠倒。请推考。 上曰。掌兵之臣。闻凶谋。不得已有此举。筵臣李公敏叙曰。初不知虚实。某之事无所失。领相金公寿恒请对言。承旨以御将密启为非。至请推。 上虽不从而某不安。玆事有曲折。设鞫数日。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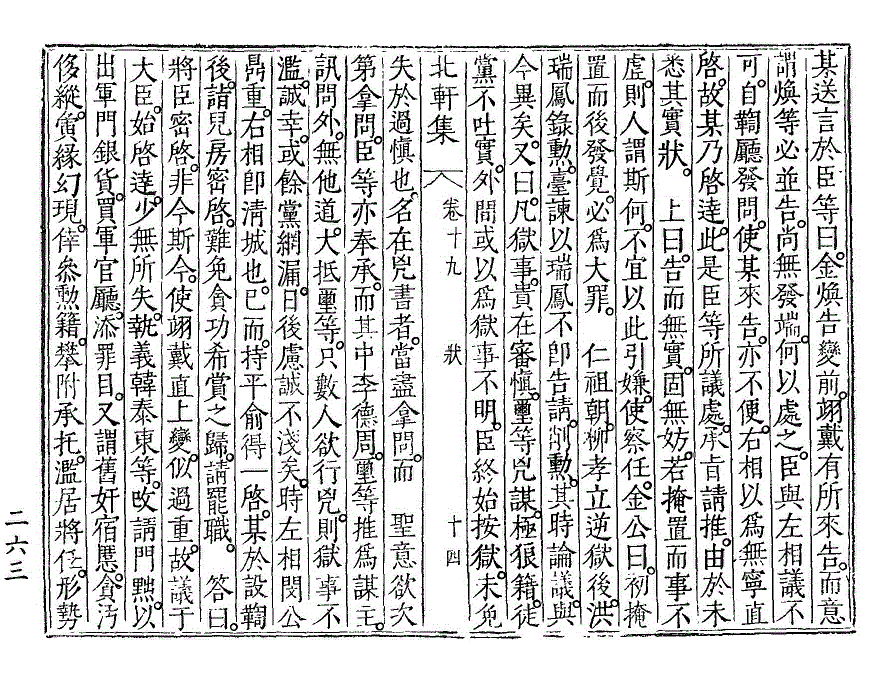 某送言于臣等曰。金焕告变前。翊戴有所来告。而意谓焕等必并告。尚无发端。何以处之。臣与左相议不可。自鞫厅发问。使某来告。亦不便。右相以为无宁直启。故某乃启达。此是臣等所议处。承旨请推。由于未悉其实状。 上曰。告而无实。固无妨。若掩置而事不虚。则人谓斯何。不宜以此引嫌。使察任。金公曰。初掩置而后发觉。必为大罪。 仁祖朝。柳孝立逆狱后。洪瑞凤录勋。台谏以瑞凤不即告请。削勋。其时论议。与今异矣。又曰。凡狱事。贵在审慎。玺等凶谋。极狼籍。徒党不吐实。外间或以为狱事不明。臣终始按狱。未免失于过慎也。名在凶书者。当尽拿问。而 圣意欲次第拿问。臣等亦奉承。而其中李德周。玺等推为谋主。讯问外。无他道。大抵玺等。只数人欲行凶。则狱事不滥。诚幸。或馀党网漏。日后虑诚不浅矣。时左相闵公鼎重。右相即清城也。已而。持平俞得一启。某于设鞫后。诣儿房密启。难免贪功希赏之归。请罢职。 答曰。将臣密启。非今斯今。使翊戴直上变。似过重。故议于大臣。始启达。少无所失。执义韩泰东等。改请门黜。以出军门银货。买军官厅。添罪目。又谓旧奸宿慝。贪污侈纵。夤缘幻现。倖参勋籍。攀附承托。滥居将位。形势
某送言于臣等曰。金焕告变前。翊戴有所来告。而意谓焕等必并告。尚无发端。何以处之。臣与左相议不可。自鞫厅发问。使某来告。亦不便。右相以为无宁直启。故某乃启达。此是臣等所议处。承旨请推。由于未悉其实状。 上曰。告而无实。固无妨。若掩置而事不虚。则人谓斯何。不宜以此引嫌。使察任。金公曰。初掩置而后发觉。必为大罪。 仁祖朝。柳孝立逆狱后。洪瑞凤录勋。台谏以瑞凤不即告请。削勋。其时论议。与今异矣。又曰。凡狱事。贵在审慎。玺等凶谋。极狼籍。徒党不吐实。外间或以为狱事不明。臣终始按狱。未免失于过慎也。名在凶书者。当尽拿问。而 圣意欲次第拿问。臣等亦奉承。而其中李德周。玺等推为谋主。讯问外。无他道。大抵玺等。只数人欲行凶。则狱事不滥。诚幸。或馀党网漏。日后虑诚不浅矣。时左相闵公鼎重。右相即清城也。已而。持平俞得一启。某于设鞫后。诣儿房密启。难免贪功希赏之归。请罢职。 答曰。将臣密启。非今斯今。使翊戴直上变。似过重。故议于大臣。始启达。少无所失。执义韩泰东等。改请门黜。以出军门银货。买军官厅。添罪目。又谓旧奸宿慝。贪污侈纵。夤缘幻现。倖参勋籍。攀附承托。滥居将位。形势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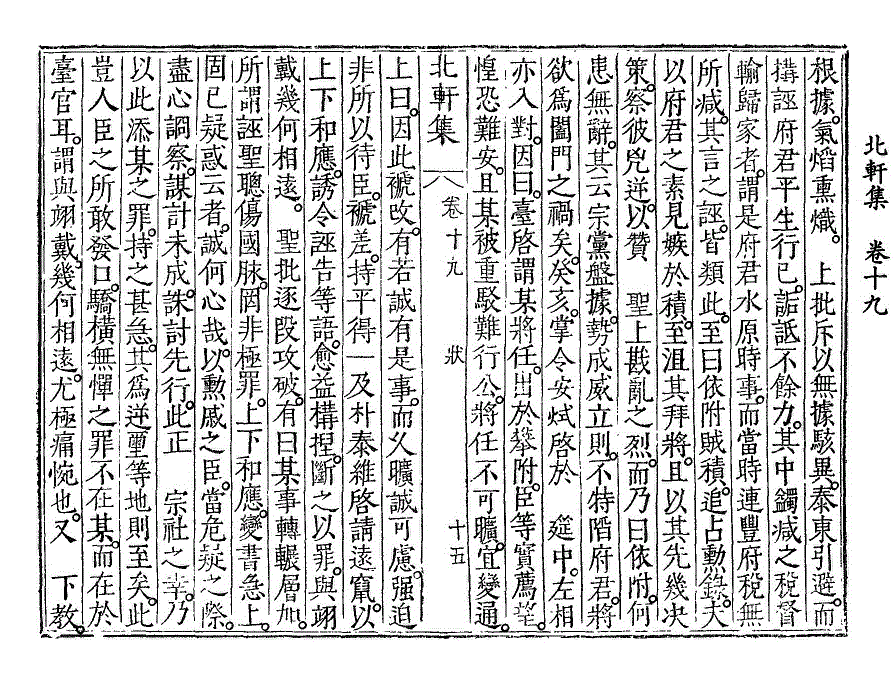 根据。气焰熏炽。 上批斥以无据骇异。泰东引避。而搆诬府君平生行己。诟诋不馀力。其中蠲减之税督输归家者。谓是府君水原时事。而当时连丰府税无所减。其言之诬。皆类此。至曰依附贼积。追占勋录。夫以府君之素见嫉于积。至沮其拜将。且以其先几决策。察彼凶逆。以赞 圣上戡乱之烈。而乃曰依附。何患无辞。其云宗党盘据。势成威立则。不特陷府君。将欲为阖门之祸矣。癸亥。掌令安烒启于 筵中。左相亦入对。因曰。台启谓某将任。出于攀附。臣等实荐望。惶恐难安。且某被重驳难行公。将任不可旷。宜变通。上曰。因此褫改。有若诚有是事。而久旷诚可虑。强迫非所以待臣。褫差。持平得一及朴泰维启请远窜。以上下和应。诱令诬告等语。愈益构捏。断之以罪。与翊戴几何相远。 圣批逐段攻破。有曰某事转辗层加。所谓诬圣聪伤国脉。罔非极罪。上下和应。变书急上。固已疑惑云者。诚何心哉。以勋戚之臣。当危疑之际。尽心诇察。谋计未成。诛讨先行。此正 宗社之幸。乃以此添某之罪。持之甚急。其为逆玺等地则至矣。此岂人臣之所敢发口。骄横无惮之罪不在某。而在于台官耳。谓与翊戴。几何相远。尤极痛惋也。又 下教。
根据。气焰熏炽。 上批斥以无据骇异。泰东引避。而搆诬府君平生行己。诟诋不馀力。其中蠲减之税督输归家者。谓是府君水原时事。而当时连丰府税无所减。其言之诬。皆类此。至曰依附贼积。追占勋录。夫以府君之素见嫉于积。至沮其拜将。且以其先几决策。察彼凶逆。以赞 圣上戡乱之烈。而乃曰依附。何患无辞。其云宗党盘据。势成威立则。不特陷府君。将欲为阖门之祸矣。癸亥。掌令安烒启于 筵中。左相亦入对。因曰。台启谓某将任。出于攀附。臣等实荐望。惶恐难安。且某被重驳难行公。将任不可旷。宜变通。上曰。因此褫改。有若诚有是事。而久旷诚可虑。强迫非所以待臣。褫差。持平得一及朴泰维启请远窜。以上下和应。诱令诬告等语。愈益构捏。断之以罪。与翊戴几何相远。 圣批逐段攻破。有曰某事转辗层加。所谓诬圣聪伤国脉。罔非极罪。上下和应。变书急上。固已疑惑云者。诚何心哉。以勋戚之臣。当危疑之际。尽心诇察。谋计未成。诛讨先行。此正 宗社之幸。乃以此添某之罪。持之甚急。其为逆玺等地则至矣。此岂人臣之所敢发口。骄横无惮之罪不在某。而在于台官耳。谓与翊戴。几何相远。尤极痛惋也。又 下教。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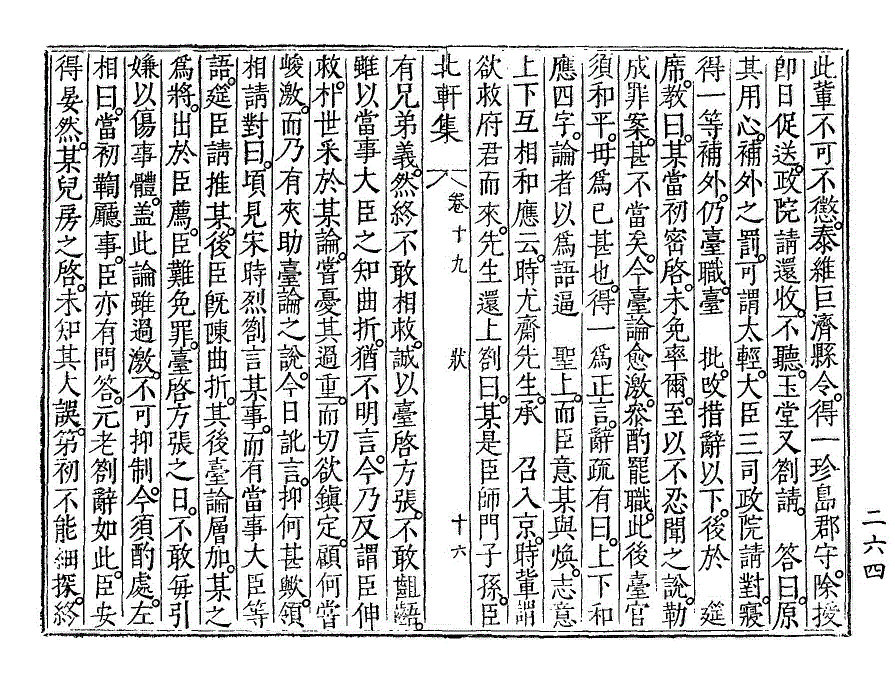 此辈不可不惩。泰维巨济县令。得一珍岛郡守。除授即日促送。政院请还收。不听。玉堂又劄请。 答曰。原其用心。补外之罚。可谓太轻。大臣三司政院请对。寝得一等补外。仍台职。台 批。改措辞以下。后于 筵席。教曰。某当初密启。未免率尔。至以不忍闻之说。勒成罪案。甚不当矣。今台论愈激。参酌罢职。此后台官须和平。毋为已甚也。得一为正言。辞疏有曰。上下和应四字。论者以为语逼 圣上。而臣意某与焕。志意上下互相和应云。时尤斋先生。承 召入京。时辈谓欲救府君而来。先生还上劄曰。某是臣师门子孙。臣有兄弟义。然终不敢相救。诚以台启方张。不敢龃龉。虽以当事大臣之知曲折。犹不明言。今乃反谓臣伸救。朴世采于某论。尝忧其过重。而切欲镇定。顾何尝峻激。而乃有夹助台论之说。今日讹言。抑何甚欤。领相请对曰。顷见宋时烈劄言某事。而有当事大臣等语。筵臣请推某。后臣既陈曲折。其后台论层加。某之为将。出于臣荐。臣难免罪。台启方张之日。不敢每引嫌以伤事体。盖此论虽过激。不可抑制。今须酌处。左相曰。当初鞫厅事。臣亦有问答。元老劄辞如此。臣安得晏然。某儿房之启。未知其大误。第初不能细探。终
此辈不可不惩。泰维巨济县令。得一珍岛郡守。除授即日促送。政院请还收。不听。玉堂又劄请。 答曰。原其用心。补外之罚。可谓太轻。大臣三司政院请对。寝得一等补外。仍台职。台 批。改措辞以下。后于 筵席。教曰。某当初密启。未免率尔。至以不忍闻之说。勒成罪案。甚不当矣。今台论愈激。参酌罢职。此后台官须和平。毋为已甚也。得一为正言。辞疏有曰。上下和应四字。论者以为语逼 圣上。而臣意某与焕。志意上下互相和应云。时尤斋先生。承 召入京。时辈谓欲救府君而来。先生还上劄曰。某是臣师门子孙。臣有兄弟义。然终不敢相救。诚以台启方张。不敢龃龉。虽以当事大臣之知曲折。犹不明言。今乃反谓臣伸救。朴世采于某论。尝忧其过重。而切欲镇定。顾何尝峻激。而乃有夹助台论之说。今日讹言。抑何甚欤。领相请对曰。顷见宋时烈劄言某事。而有当事大臣等语。筵臣请推某。后臣既陈曲折。其后台论层加。某之为将。出于臣荐。臣难免罪。台启方张之日。不敢每引嫌以伤事体。盖此论虽过激。不可抑制。今须酌处。左相曰。当初鞫厅事。臣亦有问答。元老劄辞如此。臣安得晏然。某儿房之启。未知其大误。第初不能细探。终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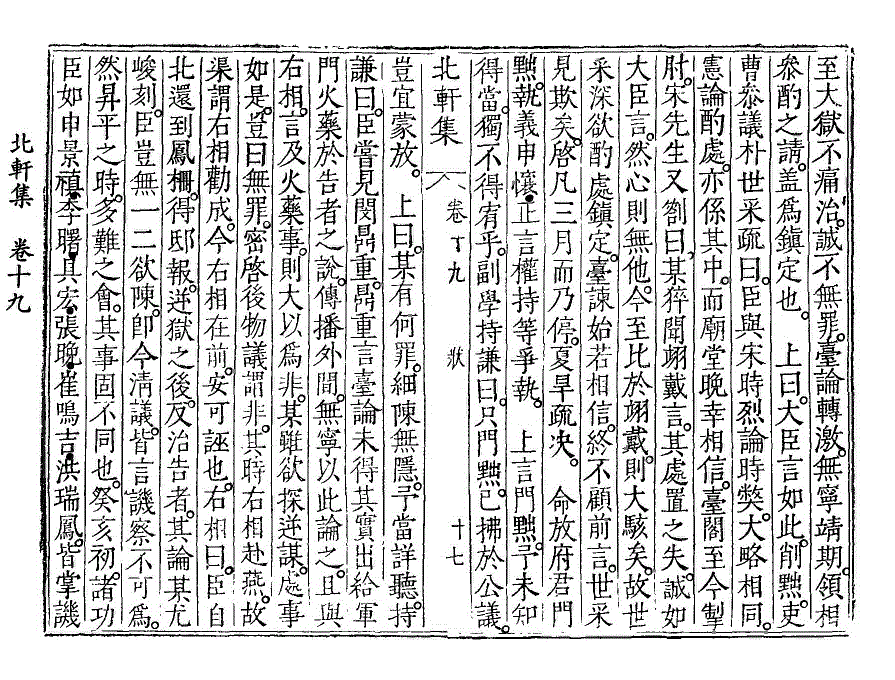 至大狱不痛治。诚不无罪。台论转激。无宁靖期。领相参酌之请。盖为镇定也。 上曰。大臣言如此。削黜。吏曹参议朴世采疏曰。臣与宋时烈论时弊。大略相同。宪论酌处。亦系其中。而庙堂晚幸相信。台阁至今掣肘。宋先生又劄曰。某猝闻翊戴言。其处置之失。诚如大臣言。然心则无他。今至比于翊戴。则大骇矣。故世采深欲酌处镇定。台谏始若相信。终不顾前言。世采见欺矣。启凡三月而乃停。夏旱疏决。 命放府君门黜。执义申懹,正言权持等争执。 上言门黜。予未知得当。独不得宥乎。副学持谦曰。只门黜。已拂于公议。岂宜蒙放。 上曰。某有何罪。细陈无隐。予当详听。持谦曰。臣尝见闵鼎重。鼎重言台论未得其实出给军门火药于告者之说。传播外间。无宁以此论之。且与右相。言及火药事。则大以为非。某虽欲探逆谋。处事如是。岂曰无罪。密启后物议谓非。其时右相赴燕。故渠谓右相劝成。今右相在前。安可诬也。右相曰。臣自北还到凤栅。得邸报。逆狱之后。反治告者。其论某尤峻刻。臣岂无一二欲陈。即今清议。皆言讥察不可为。然升平之时。多难之会。其事固不同也。癸亥初。诸功臣如申景禛,李曙,具宏,张晚,崔鸣吉,洪瑞凤。皆掌讥
至大狱不痛治。诚不无罪。台论转激。无宁靖期。领相参酌之请。盖为镇定也。 上曰。大臣言如此。削黜。吏曹参议朴世采疏曰。臣与宋时烈论时弊。大略相同。宪论酌处。亦系其中。而庙堂晚幸相信。台阁至今掣肘。宋先生又劄曰。某猝闻翊戴言。其处置之失。诚如大臣言。然心则无他。今至比于翊戴。则大骇矣。故世采深欲酌处镇定。台谏始若相信。终不顾前言。世采见欺矣。启凡三月而乃停。夏旱疏决。 命放府君门黜。执义申懹,正言权持等争执。 上言门黜。予未知得当。独不得宥乎。副学持谦曰。只门黜。已拂于公议。岂宜蒙放。 上曰。某有何罪。细陈无隐。予当详听。持谦曰。臣尝见闵鼎重。鼎重言台论未得其实出给军门火药于告者之说。传播外间。无宁以此论之。且与右相。言及火药事。则大以为非。某虽欲探逆谋。处事如是。岂曰无罪。密启后物议谓非。其时右相赴燕。故渠谓右相劝成。今右相在前。安可诬也。右相曰。臣自北还到凤栅。得邸报。逆狱之后。反治告者。其论某尤峻刻。臣岂无一二欲陈。即今清议。皆言讥察不可为。然升平之时。多难之会。其事固不同也。癸亥初。诸功臣如申景禛,李曙,具宏,张晚,崔鸣吉,洪瑞凤。皆掌讥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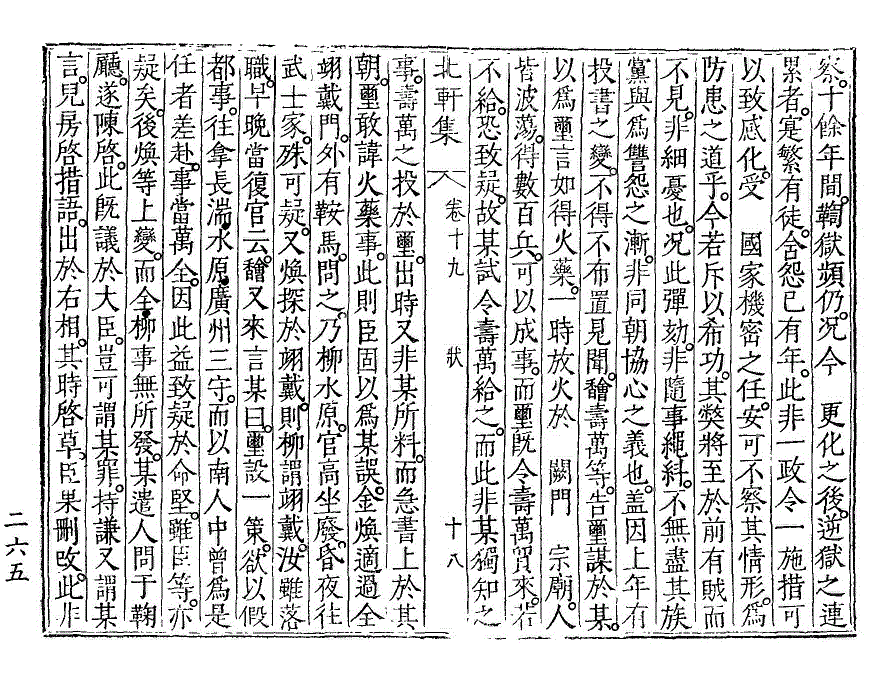 察。十馀年间。鞫狱频仍。况今 更化之后。逆狱之连累者。寔繁有徒。含怨已有年。此非一政令一施措可以致感化。受 国家机密之任。安可不察其情形。为防患之道乎。今若斥以希功。其弊将至于前有贼而不见。非细忧也。况此弹劾。非随事绳纠。不无尽其族党与为雠怨之渐。非同朝协心之义也。盖因上年有投书之变。不得不布置见闻。■(香会),寿万等。告玺谋于某。以为玺言如得火药。一时放火于 阙门 宗庙。人皆波荡。得数百兵。可以成事。而玺既令寿万贸来。若不给。恐致疑。故某试令寿万给之。而此非某独知之事。寿万之投于玺。出时又非某所料。而急书上于其朝。玺敢讳火药事。此则臣固以为某误。金焕适过全翊戴门。外有鞍马。问之。乃柳水原。官高坐废。昏夜往武士家。殊可疑。又焕探于翊戴。则柳谓翊戴。汝虽落职。早晚当复官云。■(香会)又来言某曰。玺设一策。欲以假都事。往拿长湍,水原,广州三守。而以南人中曾为是任者差赴。事当万全。因此益致疑于命坚。虽臣等。亦疑矣。后焕等上变。而全,柳事无所发。某遣人问于鞠厅。遂陈启。此既议于大臣。岂可谓某罪。持谦又谓某言。儿房启措语。出于右相。其时启草。臣果删改。此非
察。十馀年间。鞫狱频仍。况今 更化之后。逆狱之连累者。寔繁有徒。含怨已有年。此非一政令一施措可以致感化。受 国家机密之任。安可不察其情形。为防患之道乎。今若斥以希功。其弊将至于前有贼而不见。非细忧也。况此弹劾。非随事绳纠。不无尽其族党与为雠怨之渐。非同朝协心之义也。盖因上年有投书之变。不得不布置见闻。■(香会),寿万等。告玺谋于某。以为玺言如得火药。一时放火于 阙门 宗庙。人皆波荡。得数百兵。可以成事。而玺既令寿万贸来。若不给。恐致疑。故某试令寿万给之。而此非某独知之事。寿万之投于玺。出时又非某所料。而急书上于其朝。玺敢讳火药事。此则臣固以为某误。金焕适过全翊戴门。外有鞍马。问之。乃柳水原。官高坐废。昏夜往武士家。殊可疑。又焕探于翊戴。则柳谓翊戴。汝虽落职。早晚当复官云。■(香会)又来言某曰。玺设一策。欲以假都事。往拿长湍,水原,广州三守。而以南人中曾为是任者差赴。事当万全。因此益致疑于命坚。虽臣等。亦疑矣。后焕等上变。而全,柳事无所发。某遣人问于鞠厅。遂陈启。此既议于大臣。岂可谓某罪。持谦又谓某言。儿房启措语。出于右相。其时启草。臣果删改。此非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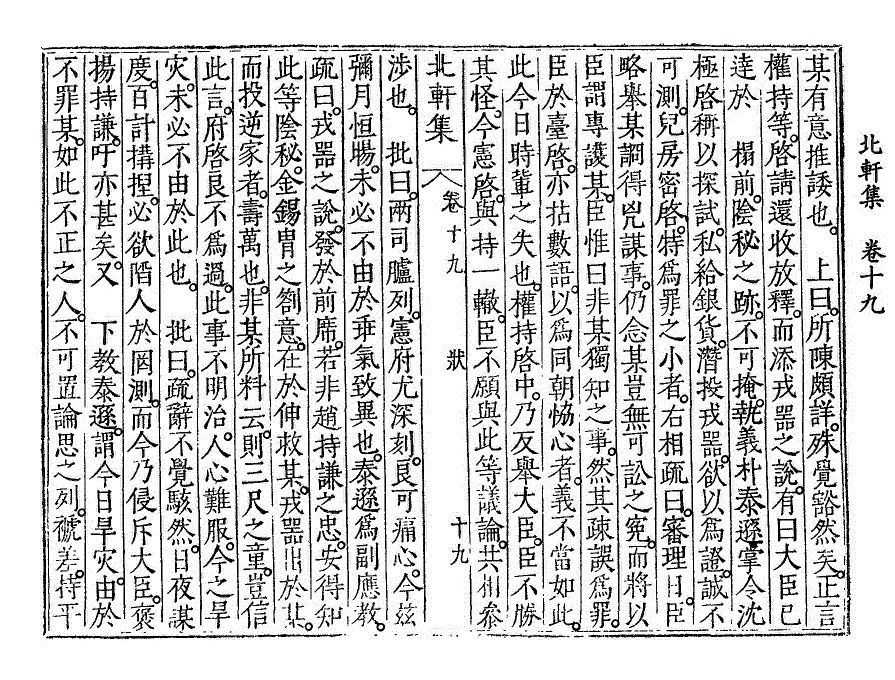 某有意推诿也。 上曰。所陈颇详。殊觉豁然矣。正言权持等。启请还收放释。而添戎器之说。有曰大臣已达于 榻前。阴秘之迹。不可掩。执义朴泰逊,掌令沈极启称以探试。私给银货。潜投戎器。欲以为證。诚不可测。儿房密启。特为罪之小者。右相疏曰。审理日。臣略举某诇得凶谋事。仍念某岂无可讼之冤。而将以臣谓专护某。臣惟曰非某独知之事。然其疏误为罪。臣于台启。亦拈数语。以为同朝协心者。义不当如此。此今日时辈之失也。权持启中。乃反举大臣。臣不胜其怪。今宪启。与持一辙。臣不愿与此等议论。共相参涉也。 批曰。两司胪列。宪府尤深刻。良可痛心。今玆弥月恒旸。未必不由于乖气致异也。泰逊为副应教。疏曰。戎器之说。发于前席。若非赵持谦之忠。安得知此等阴秘。金锡胄之劄意。在于伸救某。戎器出于某。而投逆家者。寿万也。非某所料云。则三尺之童。岂信此言。府启良不为过。此事不明治。人心难服。今之旱灾。未必不由于此也。 批曰。疏辞不觉骇然。日夜谋度。百计搆捏。必欲陷人于罔测。而今乃侵斥大臣。褒扬持谦。吁亦甚矣。又 下教泰逊。谓今日旱灾。由于不罪某。如此不正之人。不可置论思之列。褫差。持平
某有意推诿也。 上曰。所陈颇详。殊觉豁然矣。正言权持等。启请还收放释。而添戎器之说。有曰大臣已达于 榻前。阴秘之迹。不可掩。执义朴泰逊,掌令沈极启称以探试。私给银货。潜投戎器。欲以为證。诚不可测。儿房密启。特为罪之小者。右相疏曰。审理日。臣略举某诇得凶谋事。仍念某岂无可讼之冤。而将以臣谓专护某。臣惟曰非某独知之事。然其疏误为罪。臣于台启。亦拈数语。以为同朝协心者。义不当如此。此今日时辈之失也。权持启中。乃反举大臣。臣不胜其怪。今宪启。与持一辙。臣不愿与此等议论。共相参涉也。 批曰。两司胪列。宪府尤深刻。良可痛心。今玆弥月恒旸。未必不由于乖气致异也。泰逊为副应教。疏曰。戎器之说。发于前席。若非赵持谦之忠。安得知此等阴秘。金锡胄之劄意。在于伸救某。戎器出于某。而投逆家者。寿万也。非某所料云。则三尺之童。岂信此言。府启良不为过。此事不明治。人心难服。今之旱灾。未必不由于此也。 批曰。疏辞不觉骇然。日夜谋度。百计搆捏。必欲陷人于罔测。而今乃侵斥大臣。褒扬持谦。吁亦甚矣。又 下教泰逊。谓今日旱灾。由于不罪某。如此不正之人。不可置论思之列。褫差。持平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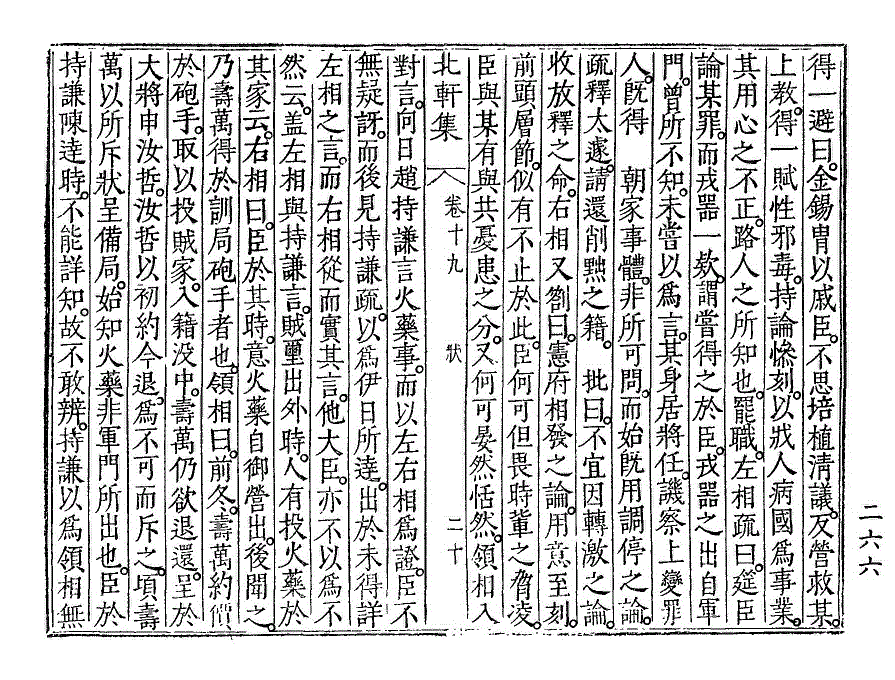 得一避曰。金锡胄以戚臣。不思培植清议。反营救某。上教。得一赋性邪毒。持论惨刻。以戕人病国为事业。其用心之不正。路人之所知也。罢职。左相疏曰。筵臣论某罪。而戎器一款。谓尝得之于臣。戎器之出自军门。曾所不知。未尝以为言。某身居将任。讥察上变罪人。既得 朝家事体。非所可问。而始既用调停之论。疏释太遽。请还削黜之籍。 批曰。不宜因转激之论。收放释之命。右相又劄曰。宪府相发之论。用意至刻。前头层节。似有不止于此。臣何可但畏时辈之胁凌。臣与某有与共忧患之分。又何可晏然恬然。领相入对言。向日赵持谦言火药事。而以左右相为證。臣不无疑讶。而后见持谦疏。以为伊日所达。出于未得详左相之言。而右相从而实其言。他大臣。亦不以为不然云。盖左相与持谦言。贼玺出外时。人有投火药于其家云。右相曰。臣于其时。意火药自御营出。后闻之。乃寿万得于训局炮手者也。领相曰。前冬。寿万约价于炮手。取以投贼家。入籍没中。寿万仍欲退还。呈于大将申汝哲。汝哲以初约今退。为不可而斥之。顷寿万以所斥状呈备局。始知火药非军门所出也。臣于持谦陈达时。不能详知。故不敢辨。持谦以为领相无
得一避曰。金锡胄以戚臣。不思培植清议。反营救某。上教。得一赋性邪毒。持论惨刻。以戕人病国为事业。其用心之不正。路人之所知也。罢职。左相疏曰。筵臣论某罪。而戎器一款。谓尝得之于臣。戎器之出自军门。曾所不知。未尝以为言。某身居将任。讥察上变罪人。既得 朝家事体。非所可问。而始既用调停之论。疏释太遽。请还削黜之籍。 批曰。不宜因转激之论。收放释之命。右相又劄曰。宪府相发之论。用意至刻。前头层节。似有不止于此。臣何可但畏时辈之胁凌。臣与某有与共忧患之分。又何可晏然恬然。领相入对言。向日赵持谦言火药事。而以左右相为證。臣不无疑讶。而后见持谦疏。以为伊日所达。出于未得详左相之言。而右相从而实其言。他大臣。亦不以为不然云。盖左相与持谦言。贼玺出外时。人有投火药于其家云。右相曰。臣于其时。意火药自御营出。后闻之。乃寿万得于训局炮手者也。领相曰。前冬。寿万约价于炮手。取以投贼家。入籍没中。寿万仍欲退还。呈于大将申汝哲。汝哲以初约今退。为不可而斥之。顷寿万以所斥状呈备局。始知火药非军门所出也。臣于持谦陈达时。不能详知。故不敢辨。持谦以为领相无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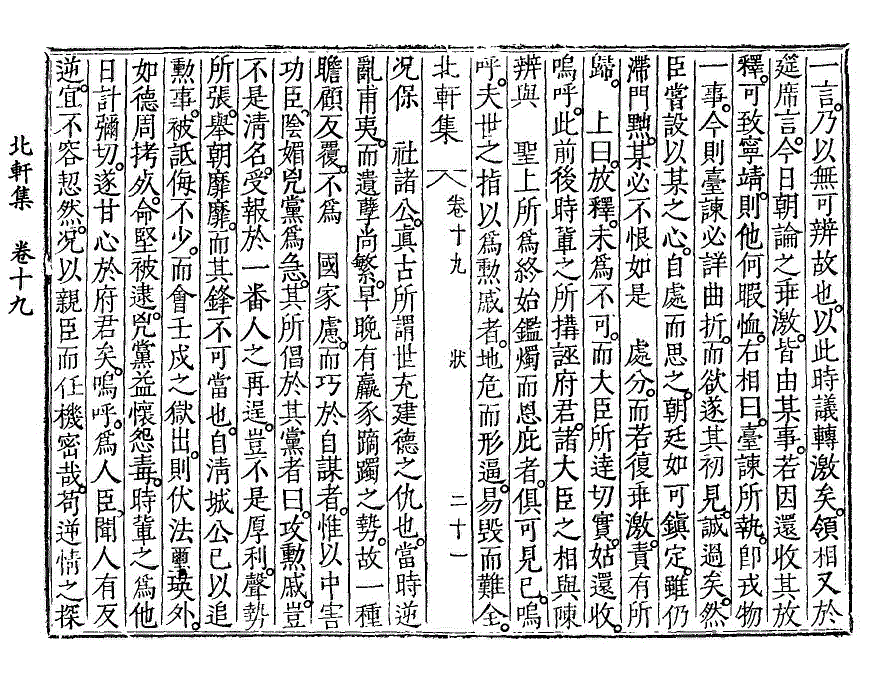 一言。乃以无可辨故也。以此时议转激矣。领相又于筵席言。今日朝论之乖激。皆由某事。若因还收其放释。可致宁靖。则他何暇恤。右相曰。台谏所执。即戎物一事。今则台谏必详曲折。而欲遂其初见。诚过矣。然臣尝设以某之心。自处而思之。朝廷如可镇定。虽仍滞门黜。某必不恨如是 处分。而若复乖激。责有所归。 上曰。放释。未为不可。而大臣所达切实。姑还收。呜呼。此前后时辈之所搆诬府君。诸大臣之相与陈辨与 圣上所为终始鉴烛而恩庇者。俱可见已。呜呼。夫世之指以为勋戚者。地危而形逼。易毁而难全。况保 社诸公。真古所谓世充建德之仇也。当时逆乱甫夷。而遗孽尚繁。早晚有羸豕蹢躅之势。故一种瞻顾反覆。不为 国家虑。而巧于自谋者。惟以中害功臣。阴媚凶党为急。其所倡于其党者曰。攻勋戚。岂不是清名。受报于一番人之再逞。岂不是厚利。声势所张。举朝靡靡。而其锋不可当也。自清城公已以追勋事。被诋侮不少。而会壬戌之狱出。则伏法玺,瑛外。如德周拷死。命坚被逮。凶党益怀怨毒。时辈之为他日计弥切。遂甘心于府君矣。呜呼。为人臣。闻人有反逆。宜不容恝然。况以亲臣而任机密哉。苟逆情之探
一言。乃以无可辨故也。以此时议转激矣。领相又于筵席言。今日朝论之乖激。皆由某事。若因还收其放释。可致宁靖。则他何暇恤。右相曰。台谏所执。即戎物一事。今则台谏必详曲折。而欲遂其初见。诚过矣。然臣尝设以某之心。自处而思之。朝廷如可镇定。虽仍滞门黜。某必不恨如是 处分。而若复乖激。责有所归。 上曰。放释。未为不可。而大臣所达切实。姑还收。呜呼。此前后时辈之所搆诬府君。诸大臣之相与陈辨与 圣上所为终始鉴烛而恩庇者。俱可见已。呜呼。夫世之指以为勋戚者。地危而形逼。易毁而难全。况保 社诸公。真古所谓世充建德之仇也。当时逆乱甫夷。而遗孽尚繁。早晚有羸豕蹢躅之势。故一种瞻顾反覆。不为 国家虑。而巧于自谋者。惟以中害功臣。阴媚凶党为急。其所倡于其党者曰。攻勋戚。岂不是清名。受报于一番人之再逞。岂不是厚利。声势所张。举朝靡靡。而其锋不可当也。自清城公已以追勋事。被诋侮不少。而会壬戌之狱出。则伏法玺,瑛外。如德周拷死。命坚被逮。凶党益怀怨毒。时辈之为他日计弥切。遂甘心于府君矣。呜呼。为人臣。闻人有反逆。宜不容恝然。况以亲臣而任机密哉。苟逆情之探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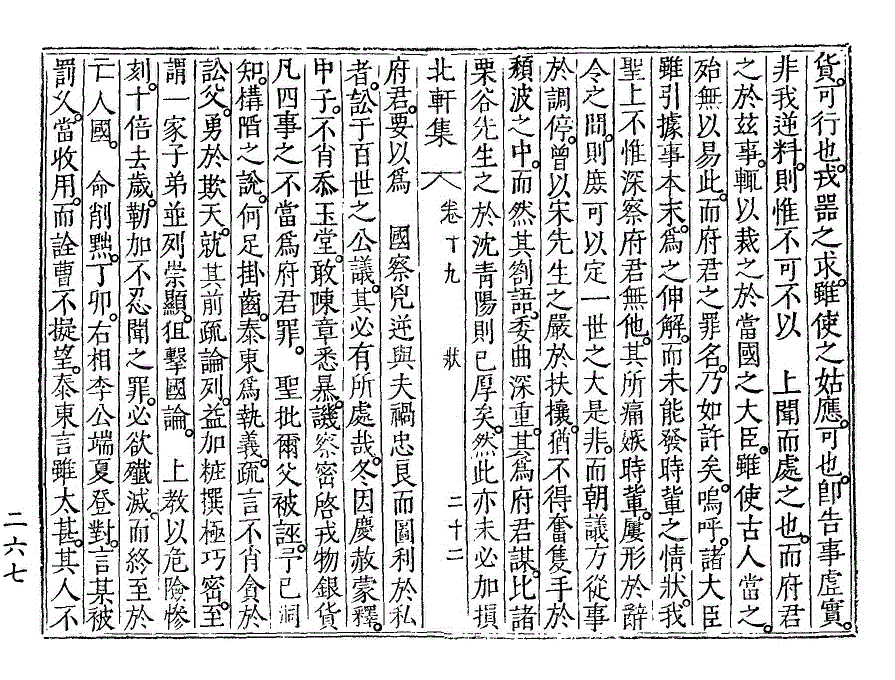 货。可行也。戎器之求。虽使之姑应。可也。即告事虚实。非我逆料。则惟不可不以 上闻而处之也。而府君之于玆事。辄以裁之于当国之大臣。虽使古人当之。殆无以易此。而府君之罪名。乃如许矣。呜呼。诸大臣虽引据事本末。为之伸解。而未能发时辈之情状。我圣上不惟深察府君无他。其所痛嫉时辈。屡形于辞令之间。则庶可以定一世之大是非。而朝议方从事于调停。曾以宋先生之严于扶攘。犹不得奋只手于颓波之中。而然其劄语。委曲深重。其为府君谋。比诸栗谷先生之于沈青阳则已厚矣。然此亦未必加损府君。要以为 国察凶逆与夫祸忠良而图利于私者。讼于百世之公议。其必有所处哉。冬因庆赦蒙释。甲子。不肖忝玉堂。敢陈章悉暴。讥察密启戎物银货凡四事之不当为府君罪。 圣批尔父被诬。予已洞知。构陷之说。何足挂齿。泰东为执义。疏言不肖贪于讼父。勇于欺天。就其前疏论列。益加妆撰极巧密。至谓一家子弟并列崇显。狙击国论。 上教以危险惨刻。十倍去岁。勒加不忍闻之罪。必欲歼灭。而终至于亡人国。 命削黜。丁卯。右相李公端夏登对。言某被罚久。当收用。而诠曹不拟望。泰东言虽太甚。其人不
货。可行也。戎器之求。虽使之姑应。可也。即告事虚实。非我逆料。则惟不可不以 上闻而处之也。而府君之于玆事。辄以裁之于当国之大臣。虽使古人当之。殆无以易此。而府君之罪名。乃如许矣。呜呼。诸大臣虽引据事本末。为之伸解。而未能发时辈之情状。我圣上不惟深察府君无他。其所痛嫉时辈。屡形于辞令之间。则庶可以定一世之大是非。而朝议方从事于调停。曾以宋先生之严于扶攘。犹不得奋只手于颓波之中。而然其劄语。委曲深重。其为府君谋。比诸栗谷先生之于沈青阳则已厚矣。然此亦未必加损府君。要以为 国察凶逆与夫祸忠良而图利于私者。讼于百世之公议。其必有所处哉。冬因庆赦蒙释。甲子。不肖忝玉堂。敢陈章悉暴。讥察密启戎物银货凡四事之不当为府君罪。 圣批尔父被诬。予已洞知。构陷之说。何足挂齿。泰东为执义。疏言不肖贪于讼父。勇于欺天。就其前疏论列。益加妆撰极巧密。至谓一家子弟并列崇显。狙击国论。 上教以危险惨刻。十倍去岁。勒加不忍闻之罪。必欲歼灭。而终至于亡人国。 命削黜。丁卯。右相李公端夏登对。言某被罚久。当收用。而诠曹不拟望。泰东言虽太甚。其人不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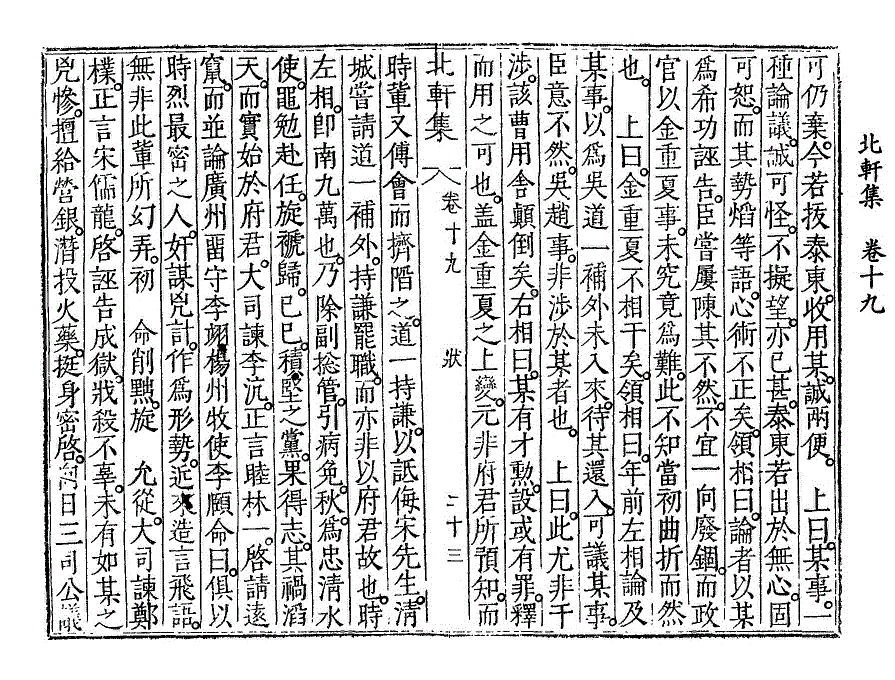 可仍弃。今若拔泰东。收用某。诚两便。 上曰。某事。一种论议。诚可怪。不拟望。亦已甚。泰东若出于无心。固可恕。而其势焰等语。心术不正矣。领相曰。论者以某为希功诬告。臣尝屡陈其不然。不宜一向废锢。而政官以金重夏事。未究竟为难。此不知当初曲折而然也。 上曰。金重夏不相干矣。领相曰。年前左相论及某事。以为吴道一补外未入来。待其还入。可议某事。臣意不然。吴赵事。非涉于某者也。 上曰。此尤非干涉。该曹用舍颠倒矣。右相曰。某有才勋。设或有罪。释而用之可也。盖金重夏之上变。元非府君所预知。而时辈又傅会而挤陷之。道一持谦。以诋侮宋先生。清城尝请道一补外。持谦罢职。而亦非以府君故也。时左相。即南九万也。乃除副总管。引病免。秋。为忠清水使。黾勉赴任。旋褫归。己巳。积,坚之党。果得志。其祸滔天。而实始于府君。大司谏李沆。正言睦林一。启请远窜。而并论广州留守李翊,杨州牧使李颐命曰。俱以时烈最密之人。奸谋凶计。作为形势。近来造言飞语。无非此辈所幻弄。初 命削黜。旋 允从。大司谏郑朴。正言宋儒龙。启诬告成狱。戕杀不辜。未有如某之凶惨。擅给营银。潜投火药。挺身密启。向日三司公议
可仍弃。今若拔泰东。收用某。诚两便。 上曰。某事。一种论议。诚可怪。不拟望。亦已甚。泰东若出于无心。固可恕。而其势焰等语。心术不正矣。领相曰。论者以某为希功诬告。臣尝屡陈其不然。不宜一向废锢。而政官以金重夏事。未究竟为难。此不知当初曲折而然也。 上曰。金重夏不相干矣。领相曰。年前左相论及某事。以为吴道一补外未入来。待其还入。可议某事。臣意不然。吴赵事。非涉于某者也。 上曰。此尤非干涉。该曹用舍颠倒矣。右相曰。某有才勋。设或有罪。释而用之可也。盖金重夏之上变。元非府君所预知。而时辈又傅会而挤陷之。道一持谦。以诋侮宋先生。清城尝请道一补外。持谦罢职。而亦非以府君故也。时左相。即南九万也。乃除副总管。引病免。秋。为忠清水使。黾勉赴任。旋褫归。己巳。积,坚之党。果得志。其祸滔天。而实始于府君。大司谏李沆。正言睦林一。启请远窜。而并论广州留守李翊,杨州牧使李颐命曰。俱以时烈最密之人。奸谋凶计。作为形势。近来造言飞语。无非此辈所幻弄。初 命削黜。旋 允从。大司谏郑朴。正言宋儒龙。启诬告成狱。戕杀不辜。未有如某之凶惨。擅给营银。潜投火药。挺身密启。向日三司公议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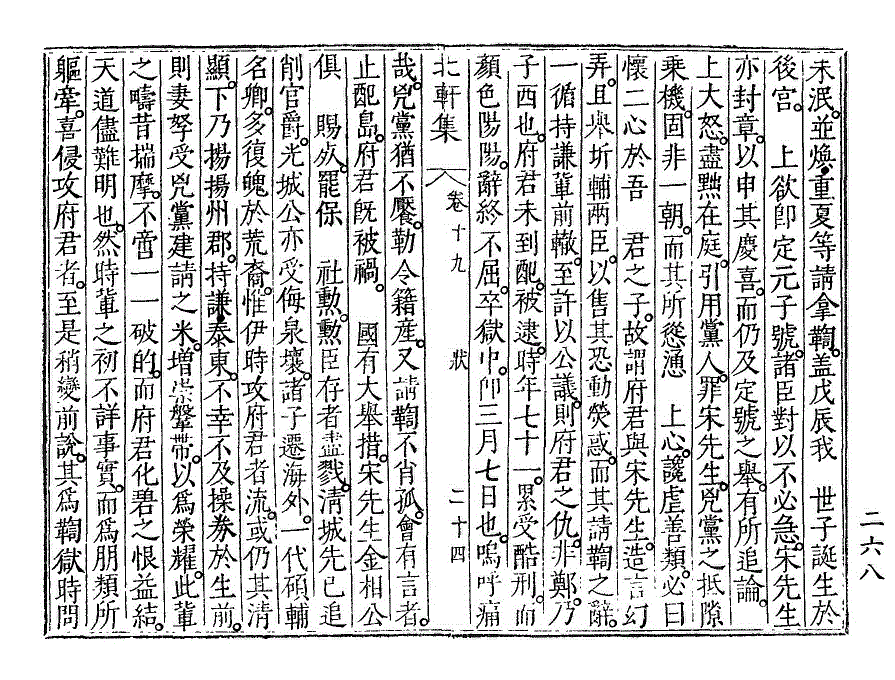 未泯。并焕,重夏等请拿鞫。盖戊辰我 世子诞生于后宫。 上欲即定元子号。诸臣对以不必急。宋先生亦封章。以申其庆喜。而仍及定号之举。有所追论。 上大怒。尽黜在庭。引用党人。罪宋先生。凶党之抵隙乘机。固非一朝。而其所怂恿 上心。谗虐善类。必曰怀二心于吾 君之子。故谓府君与宋先生。造言幻弄。且举圻辅两臣。以售其恐动荧惑。而其请鞫之辞。一循持谦辈前辙。至许以公议。则府君之仇。非郑。乃子西也。府君未到配。被逮。时年七十一。累受酷刑。而颜色阳阳。辞终不屈。卒狱中。即三月七日也。呜呼痛哉。凶党犹不餍。勒令籍产。又请鞫不肖孤。会有言者。止配岛。府君既被祸。 国有大举措。宋先生金相公俱 赐死。罢保 社勋。勋臣存者尽戮。清城先已追削官爵。光城公亦受侮泉壤。诸子迁海外。一代硕辅名卿。多复魄于荒裔。惟伊时攻府君者流。或仍其清显。下乃扬扬州郡。持谦,泰东。不幸不及操券于生前。则妻孥受凶党建请之米。增崇鞶带。以为荣耀。此辈之畴昔揣摩。不啻一一破的。而府君化碧之恨益结。天道尽难明也。然时辈之初不详事实。而为朋类所躯牵。喜侵攻府君者。至是稍变前说。其为鞫狱时问
未泯。并焕,重夏等请拿鞫。盖戊辰我 世子诞生于后宫。 上欲即定元子号。诸臣对以不必急。宋先生亦封章。以申其庆喜。而仍及定号之举。有所追论。 上大怒。尽黜在庭。引用党人。罪宋先生。凶党之抵隙乘机。固非一朝。而其所怂恿 上心。谗虐善类。必曰怀二心于吾 君之子。故谓府君与宋先生。造言幻弄。且举圻辅两臣。以售其恐动荧惑。而其请鞫之辞。一循持谦辈前辙。至许以公议。则府君之仇。非郑。乃子西也。府君未到配。被逮。时年七十一。累受酷刑。而颜色阳阳。辞终不屈。卒狱中。即三月七日也。呜呼痛哉。凶党犹不餍。勒令籍产。又请鞫不肖孤。会有言者。止配岛。府君既被祸。 国有大举措。宋先生金相公俱 赐死。罢保 社勋。勋臣存者尽戮。清城先已追削官爵。光城公亦受侮泉壤。诸子迁海外。一代硕辅名卿。多复魄于荒裔。惟伊时攻府君者流。或仍其清显。下乃扬扬州郡。持谦,泰东。不幸不及操券于生前。则妻孥受凶党建请之米。增崇鞶带。以为荣耀。此辈之畴昔揣摩。不啻一一破的。而府君化碧之恨益结。天道尽难明也。然时辈之初不详事实。而为朋类所躯牵。喜侵攻府君者。至是稍变前说。其为鞫狱时问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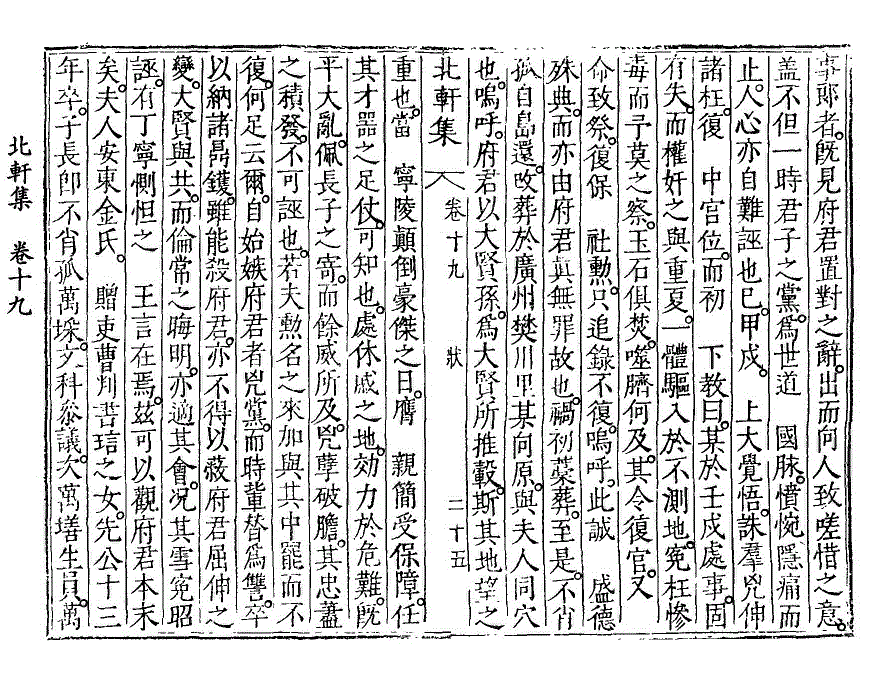 事郎者。既见府君置对之辞。出而向人致嗟惜之意。盖不但一时君子之党。为世道 国脉。愤惋隐痛而止。人心亦自难诬也已。甲戌。 上大觉悟。诛群凶伸诸枉。复 中宫位。而初 下教曰。某于壬戌处事。固有失。而权奸之与重夏。一体驱入于不测地。冤枉惨毒而予莫之察。玉石俱焚。噬脐何及。其令复官。又 命致祭。复保 社勋。只追录不复。呜呼。此诚 盛德殊典。而亦由府君真无罪故也。祸初藁葬。至是。不肖孤自岛还。改葬于广州樊川里某向原。与夫人同穴也。呜呼。府君以大贤孙。为大贤所推毂。斯其地望之重也。当 宁陵颠倒豪杰之日。膺 亲简受保障。任其才器之足仗。可知也。处休戚之地。效力于危难。既平大乱。佩长子之寄。而馀威所及。凶孽破胆。其忠荩之积发。不可诬也。若夫勋名之来加与其中罢而不复。何足云尔。自始嫉府君者凶党。而时辈替为雠。卒以纳诸鼎镬。虽能杀府君。亦不得以蔽府君屈伸之变。大贤与共。而伦常之晦明。亦适其会。况其雪冤昭诬。有丁宁恻怛之 王言在焉。玆可以观府君本末矣。夫人安东金氏。 赠吏曹判书琂之女。先公十三年卒。子长即不肖孤万埰。文科参议。次万墡生员。万
事郎者。既见府君置对之辞。出而向人致嗟惜之意。盖不但一时君子之党。为世道 国脉。愤惋隐痛而止。人心亦自难诬也已。甲戌。 上大觉悟。诛群凶伸诸枉。复 中宫位。而初 下教曰。某于壬戌处事。固有失。而权奸之与重夏。一体驱入于不测地。冤枉惨毒而予莫之察。玉石俱焚。噬脐何及。其令复官。又 命致祭。复保 社勋。只追录不复。呜呼。此诚 盛德殊典。而亦由府君真无罪故也。祸初藁葬。至是。不肖孤自岛还。改葬于广州樊川里某向原。与夫人同穴也。呜呼。府君以大贤孙。为大贤所推毂。斯其地望之重也。当 宁陵颠倒豪杰之日。膺 亲简受保障。任其才器之足仗。可知也。处休戚之地。效力于危难。既平大乱。佩长子之寄。而馀威所及。凶孽破胆。其忠荩之积发。不可诬也。若夫勋名之来加与其中罢而不复。何足云尔。自始嫉府君者凶党。而时辈替为雠。卒以纳诸鼎镬。虽能杀府君。亦不得以蔽府君屈伸之变。大贤与共。而伦常之晦明。亦适其会。况其雪冤昭诬。有丁宁恻怛之 王言在焉。玆可以观府君本末矣。夫人安东金氏。 赠吏曹判书琂之女。先公十三年卒。子长即不肖孤万埰。文科参议。次万墡生员。万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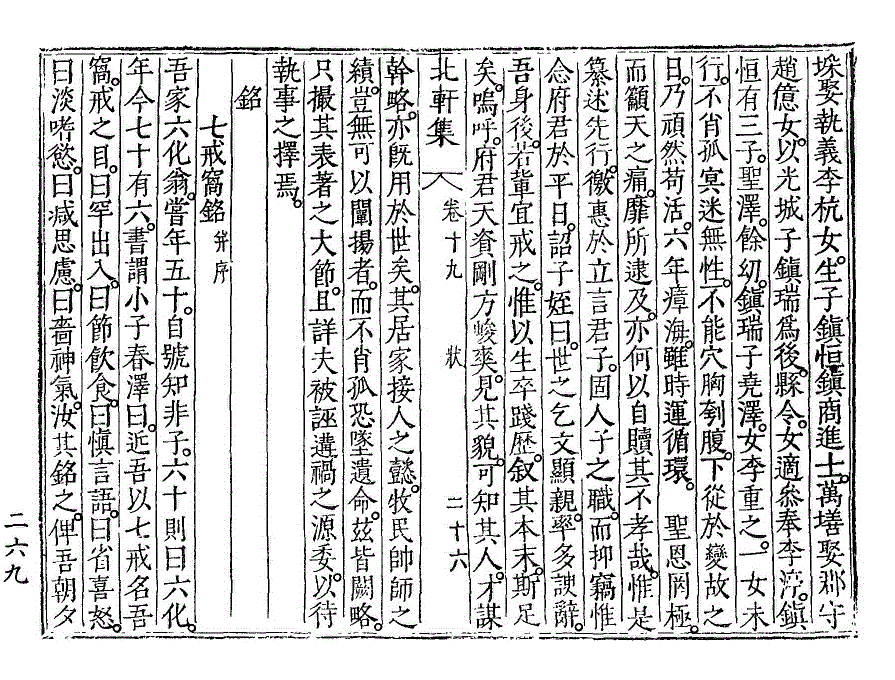 埰娶执义李杭女。生子镇恒,镇商进士。万墡娶郡守赵亿女。以光城子镇瑞为后。县令。女适参奉李渟。镇恒有三子。圣泽。馀幼。镇瑞子尧泽。女李重之。一女未行。不肖孤冥迷无性。不能穴胸刳腹。下从于变故之日。乃顽然苟活。六年瘴海。虽时运循环。 圣恩罔极。而吁天之痛。靡所逮及。亦何以自赎其不孝哉。惟是纂述先行。徼惠于立言君子。固人子之职。而抑窃惟念府君于平日。诏子侄曰。世之乞文显亲。率多谀辞。吾身后。若辈宜戒之。惟以生卒践历。叙其本末。斯足矣。呜呼。府君天资刚方峻爽。见其貌。可知其人。才谋干略。亦既用于世矣。其居家接人之懿。牧民帅师之绩。岂无可以阐扬者。而不肖孤恐坠遗命。玆皆阙略。只撮其表著之大节。且详夫被诬遘祸之源委。以待执事之择焉。
埰娶执义李杭女。生子镇恒,镇商进士。万墡娶郡守赵亿女。以光城子镇瑞为后。县令。女适参奉李渟。镇恒有三子。圣泽。馀幼。镇瑞子尧泽。女李重之。一女未行。不肖孤冥迷无性。不能穴胸刳腹。下从于变故之日。乃顽然苟活。六年瘴海。虽时运循环。 圣恩罔极。而吁天之痛。靡所逮及。亦何以自赎其不孝哉。惟是纂述先行。徼惠于立言君子。固人子之职。而抑窃惟念府君于平日。诏子侄曰。世之乞文显亲。率多谀辞。吾身后。若辈宜戒之。惟以生卒践历。叙其本末。斯足矣。呜呼。府君天资刚方峻爽。见其貌。可知其人。才谋干略。亦既用于世矣。其居家接人之懿。牧民帅师之绩。岂无可以阐扬者。而不肖孤恐坠遗命。玆皆阙略。只撮其表著之大节。且详夫被诬遘祸之源委。以待执事之择焉。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铭
七戒窝铭(并序)
吾家六化翁。尝年五十。自号知非子。六十则曰六化。年今七十有六。书谓小子春泽曰。近吾以七戒名吾窝。戒之目。曰罕出入。曰节饮食。曰慎言语。曰省喜怒。曰淡嗜欲。曰减思虑。曰啬神气。汝其铭之。俾吾朝夕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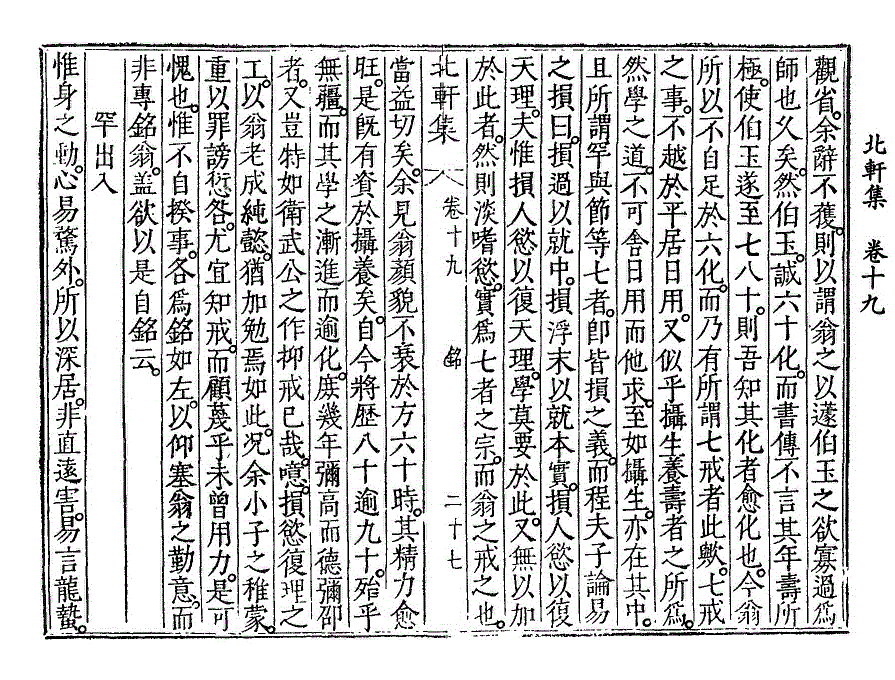 观省。余辞不获。则以谓翁之以蘧伯玉之欲寡过为师也久矣。然伯玉。诚六十化。而书传不言其年寿所极。使伯玉遂至七八十。则吾知其化者愈化也。今翁所以不自足于六化。而乃有所谓七戒者此欤。七戒之事。不越于平居日用。又似乎摄生养寿者之所为。然学之道。不可舍日用而他求。至如摄生。亦在其中。且所谓罕与节等七者。即皆损之义。而程夫子论易之损曰。损过以就中。损浮末以就本实。损人欲以复天理。夫惟损人欲以复天理。学莫要于此。又无以加于此者。然则淡嗜欲。实为七者之宗。而翁之戒之也。当益切矣。余见翁颜貌不衰于方六十时。其精力愈旺。是既有资于摄养矣。自今将历八十逾九十。殆乎无疆。而其学之渐进而逾化。庶几年弥高而德弥卲者。又岂特如卫武公之作抑戒已哉。噫。损欲复理之工。以翁老成纯懿。犹加勉焉如此。况余小子之稚蒙。重以罪谤愆咎。尤宜知戒。而顾蔑乎未曾用力。是可愧也。惟不自揆事。各为铭如左。以仰塞翁之勤意。而非专铭翁。盖欲以是自铭云。
观省。余辞不获。则以谓翁之以蘧伯玉之欲寡过为师也久矣。然伯玉。诚六十化。而书传不言其年寿所极。使伯玉遂至七八十。则吾知其化者愈化也。今翁所以不自足于六化。而乃有所谓七戒者此欤。七戒之事。不越于平居日用。又似乎摄生养寿者之所为。然学之道。不可舍日用而他求。至如摄生。亦在其中。且所谓罕与节等七者。即皆损之义。而程夫子论易之损曰。损过以就中。损浮末以就本实。损人欲以复天理。夫惟损人欲以复天理。学莫要于此。又无以加于此者。然则淡嗜欲。实为七者之宗。而翁之戒之也。当益切矣。余见翁颜貌不衰于方六十时。其精力愈旺。是既有资于摄养矣。自今将历八十逾九十。殆乎无疆。而其学之渐进而逾化。庶几年弥高而德弥卲者。又岂特如卫武公之作抑戒已哉。噫。损欲复理之工。以翁老成纯懿。犹加勉焉如此。况余小子之稚蒙。重以罪谤愆咎。尤宜知戒。而顾蔑乎未曾用力。是可愧也。惟不自揆事。各为铭如左。以仰塞翁之勤意。而非专铭翁。盖欲以是自铭云。罕出入
惟身之动。心易骛外。所以深居。非直远害。易言龙蛰。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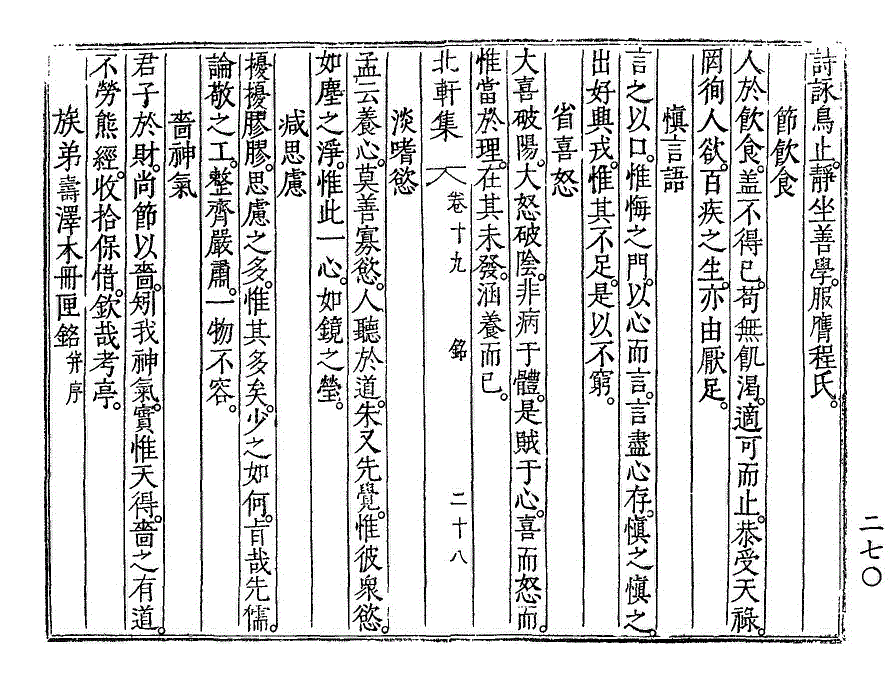 诗咏鸟止。静坐善学。服膺程氏。
诗咏鸟止。静坐善学。服膺程氏。节饮食
人于饮食。盖不得已。苟无饥渴。适可而止。恭受天禄。罔徇人欲。百疾之生。亦由厌足。
慎言语
言之以口。惟悔之门。以心而言。言尽心存。慎之慎之。出好兴戎。惟其不足。是以不穷。
省喜怒
大喜破阳。大怒破阴。非病于体。是贼于心。喜而怒而。惟当于理。在其未发。涵养而已。
淡嗜欲
孟云养心。莫善寡欲。人听于道。朱又先觉。惟彼众欲。如尘之净。惟此一心。如镜之莹。
减思虑
扰扰胶胶。思虑之多。惟其多矣。少之如何。旨哉先儒。论敬之工。整齐严肃。一物不容。
啬神气
君子于财。尚节以啬。矧我神气。实惟天得。啬之有道。不劳熊经。收拾保惜。钦哉考亭。
族弟寿泽木册匣铭(并序)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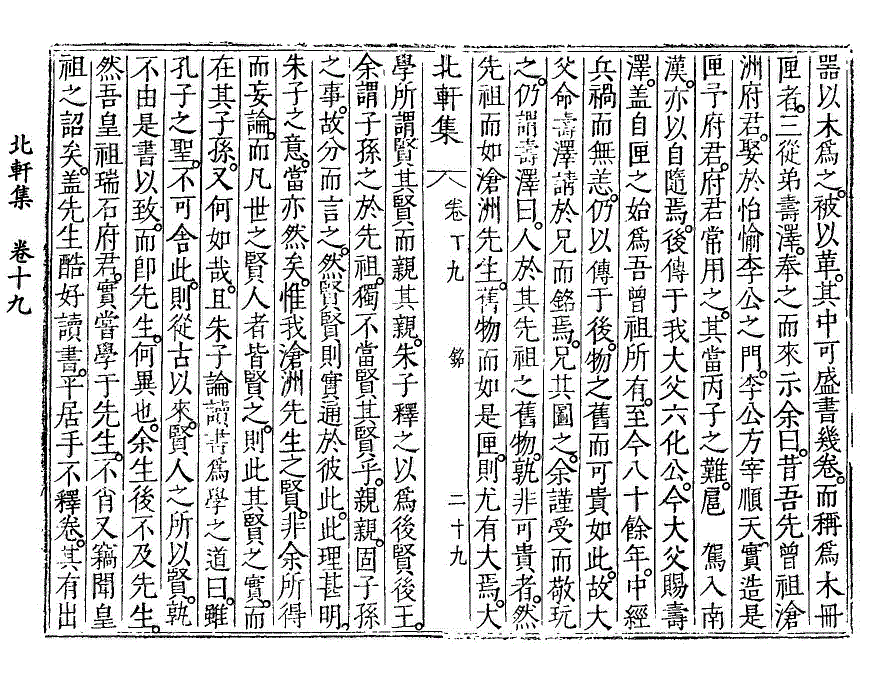 器以木为之。被以革。其中可盛书几卷。而称为木册匣者。三从弟寿泽。奉之而来示余曰。昔吾先曾祖沧洲府君。娶于怡愉李公之门。李公方宰顺天。实造是匣予府君。府君常用之。其当丙子之难。扈 驾入南汉。亦以自随焉。后传于我大父六化公。今大父赐寿泽。盖自匣之始为吾曾祖所有。至今八十馀年。中经兵祸而无恙。仍以传于后。物之旧而可贵如此。故大父命寿泽请于兄而铭焉。兄其图之。余谨受而敬玩之。仍谓寿泽曰。人于其先祖之旧物。孰非可贵者。然先祖而如沧洲先生。旧物而如是匣。则尤有大焉。大学所谓贤其贤而亲其亲。朱子释之以为后贤后王。余谓子孙之于先祖。独不当贤其贤乎。亲亲。固子孙之事。故分而言之。然贤贤则实通于彼此。此理甚明。朱子之意。当亦然矣。惟我沧洲先生之贤。非余所得而妄论。而凡世之贤人者皆贤之。则此其贤之实。而在其子孙。又何如哉。且朱子论读书为学之道曰。虽孔子之圣。不可舍此。则从古以来。贤人之所以贤。孰不由是书以致。而即先生。何异也。余生后不及先生。然吾皇祖瑞石府君。实尝学于先生。不肖又窃闻皇祖之诏矣。盖先生酷好读书。平居手不释卷。其有出
器以木为之。被以革。其中可盛书几卷。而称为木册匣者。三从弟寿泽。奉之而来示余曰。昔吾先曾祖沧洲府君。娶于怡愉李公之门。李公方宰顺天。实造是匣予府君。府君常用之。其当丙子之难。扈 驾入南汉。亦以自随焉。后传于我大父六化公。今大父赐寿泽。盖自匣之始为吾曾祖所有。至今八十馀年。中经兵祸而无恙。仍以传于后。物之旧而可贵如此。故大父命寿泽请于兄而铭焉。兄其图之。余谨受而敬玩之。仍谓寿泽曰。人于其先祖之旧物。孰非可贵者。然先祖而如沧洲先生。旧物而如是匣。则尤有大焉。大学所谓贤其贤而亲其亲。朱子释之以为后贤后王。余谓子孙之于先祖。独不当贤其贤乎。亲亲。固子孙之事。故分而言之。然贤贤则实通于彼此。此理甚明。朱子之意。当亦然矣。惟我沧洲先生之贤。非余所得而妄论。而凡世之贤人者皆贤之。则此其贤之实。而在其子孙。又何如哉。且朱子论读书为学之道曰。虽孔子之圣。不可舍此。则从古以来。贤人之所以贤。孰不由是书以致。而即先生。何异也。余生后不及先生。然吾皇祖瑞石府君。实尝学于先生。不肖又窃闻皇祖之诏矣。盖先生酷好读书。平居手不释卷。其有出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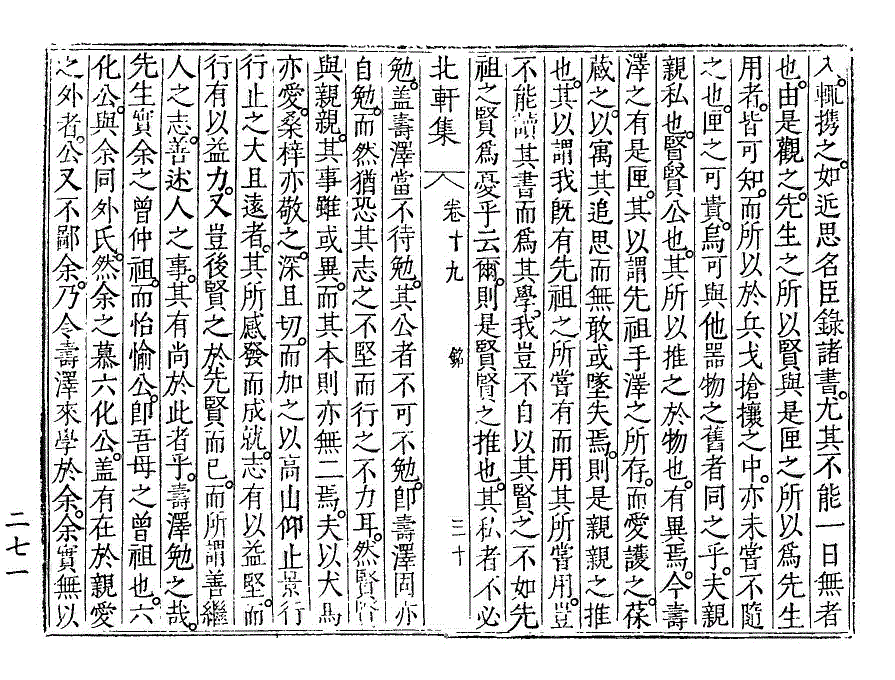 入。辄携之。如近思名臣录诸书。尤其不能一日无者也。由是观之。先生之所以贤与是匣之所以为先生用者。皆可知。而所以于兵戈抢攘之中。亦未尝不随之也。匣之可贵。乌可与他器物之旧者同之乎。夫亲亲私也。贤贤公也。其所以推之于物也。有异焉。今寿泽之有是匣。其以谓先祖手泽之所存。而爱护之。葆藏之。以寓其追思而无敢或坠失焉。则是亲亲之推也。其以谓我既有先祖之所尝有而用其所尝用。岂不能读其书而为其学。我岂不自以其贤之不如先祖之贤为忧乎云尔。则是贤贤之推也。其私者不必勉。盖寿泽当不待勉。其公者不可不勉。即寿泽固亦自勉。而然犹恐其志之不坚而行之不力耳。然贤贤与亲亲。其事虽或异。而其本则亦无二焉。夫以犬马亦爱。桑梓亦敬之。深且切。而加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大且远者。其所感发而成就。志有以益坚。而行有以益力。又岂后贤之于先贤而已。而所谓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有尚于此者乎。寿泽勉之哉。先生实余之曾仲祖。而怡愉公。即吾母之曾祖也。六化公。与余同外氏。然余之慕六化公。盖有在于亲爱之外者。公又不鄙余。乃令寿泽来学于余。余实无以
入。辄携之。如近思名臣录诸书。尤其不能一日无者也。由是观之。先生之所以贤与是匣之所以为先生用者。皆可知。而所以于兵戈抢攘之中。亦未尝不随之也。匣之可贵。乌可与他器物之旧者同之乎。夫亲亲私也。贤贤公也。其所以推之于物也。有异焉。今寿泽之有是匣。其以谓先祖手泽之所存。而爱护之。葆藏之。以寓其追思而无敢或坠失焉。则是亲亲之推也。其以谓我既有先祖之所尝有而用其所尝用。岂不能读其书而为其学。我岂不自以其贤之不如先祖之贤为忧乎云尔。则是贤贤之推也。其私者不必勉。盖寿泽当不待勉。其公者不可不勉。即寿泽固亦自勉。而然犹恐其志之不坚而行之不力耳。然贤贤与亲亲。其事虽或异。而其本则亦无二焉。夫以犬马亦爱。桑梓亦敬之。深且切。而加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大且远者。其所感发而成就。志有以益坚。而行有以益力。又岂后贤之于先贤而已。而所谓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有尚于此者乎。寿泽勉之哉。先生实余之曾仲祖。而怡愉公。即吾母之曾祖也。六化公。与余同外氏。然余之慕六化公。盖有在于亲爱之外者。公又不鄙余。乃令寿泽来学于余。余实无以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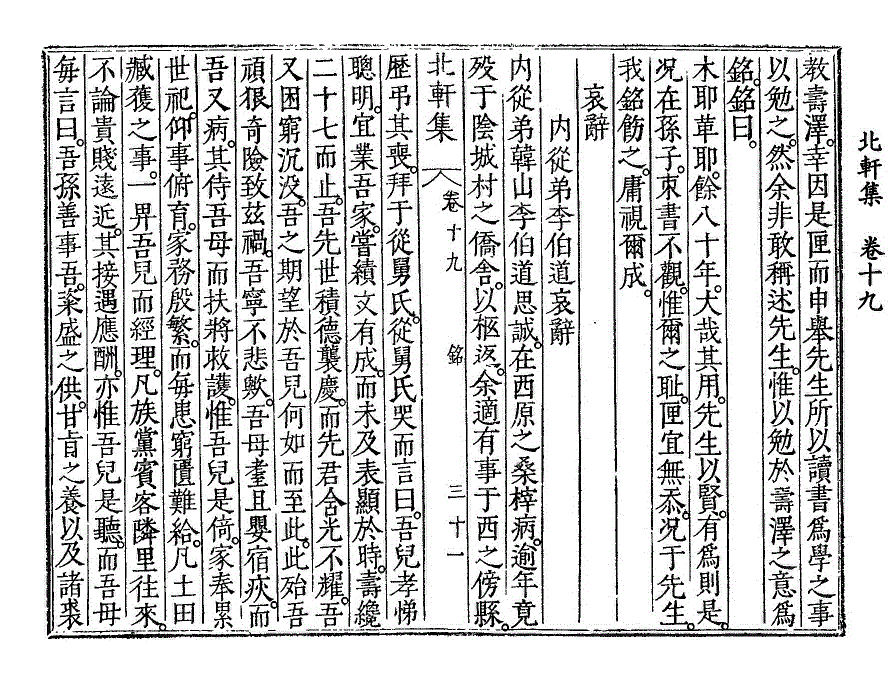 教寿泽。幸因是匣而申举先生所以读书为学之事以勉之。然余非敢称述先生。惟以勉于寿泽之意为铭。铭曰。
教寿泽。幸因是匣而申举先生所以读书为学之事以勉之。然余非敢称述先生。惟以勉于寿泽之意为铭。铭曰。木耶革耶。馀八十年。大哉其用。先生以贤。有为则是。况在孙子。束书不观。惟尔之耻。匣宜无忝。况于先生。我铭饬之。庸视尔成。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哀辞
内从弟李伯道哀辞
内从弟韩山李伯道思诚。在西原之桑梓病。逾年竟殁于阴城村之侨舍。以柩返。余适有事于西之傍县。历吊其丧。拜于从舅氏。从舅氏哭而言曰。吾儿孝悌聪明。宜业吾家。尝绩文有成。而未及表显于时。寿才二十七而止。吾先世积德袭庆。而先君含光不耀。吾又困穷沉没。吾之期望于吾儿何如而至此。此殆吾顽狠奇险致玆祸。吾宁不悲欤。吾母耋且婴宿疢。而吾又病。其侍吾母而扶将救护。惟吾儿是倚。家奉累世祀。仰事俯育。家务殷繁。而每患穷匮难给。凡土田臧获之事。一畀吾儿而经理。凡族党宾客邻里往来。不论贵贱远近。其接遇应酬。亦惟吾儿是听。而吾母每言曰。吾孙善事吾。粢盛之供。甘旨之养以及诸裘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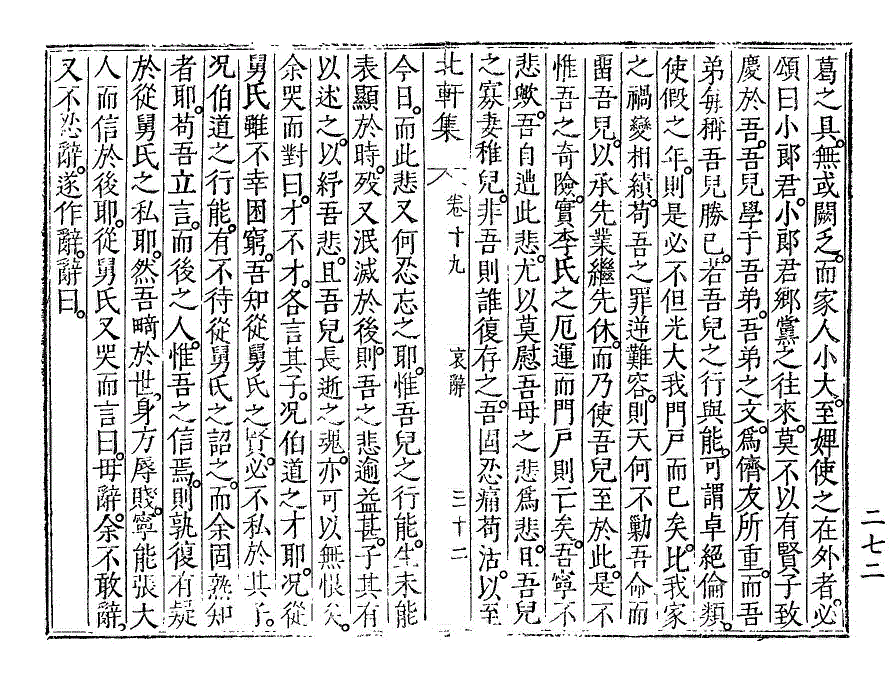 葛之具。无或阙乏。而家人小大。至婢使之在外者。必颂曰小郎君。小郎君乡党之往来。莫不以有贤子致庆于吾。吾儿学于吾弟。吾弟之文。为侪友所重。而吾弟每称吾儿胜己。若吾儿之行与能。可谓卓绝伦类。使假之年。则是必不但光大我门户而已矣。比我家之祸变相绩。苟吾之罪逆难容。则天何不剿吾命而留吾儿。以承先业继先休。而乃使吾儿至于此。是不惟吾之奇险。实李氏之厄运而门户则亡矣。吾宁不悲欤。吾自遭此悲。尤以莫慰吾母之悲为悲。且吾儿之寡妻稚儿。非吾则谁复存之。吾固忍痛苟活。以至今日。而此悲又何忍忘之耶。惟吾儿之行能。生未能表显于时。殁又泯灭于后。则吾之悲逾益甚。子其有以述之。以纾吾悲。且吾儿长逝之魂。亦可以无恨矣。余哭而对曰。才不才。各言其子。况伯道之才耶。况从舅氏虽不幸困穷。吾知从舅氏之贤。必不私于其子。况伯道之行能。有不待从舅氏之诏之。而余固熟知者耶。苟吾立言。而后之人。惟吾之信焉。则孰复有疑于从舅氏之私耶。然吾畸于世。身方辱贱。宁能张大人而信于后耶。从舅氏又哭而言曰。毋辞。余不敢辞。又不忍辞。遂作辞。辞曰。
葛之具。无或阙乏。而家人小大。至婢使之在外者。必颂曰小郎君。小郎君乡党之往来。莫不以有贤子致庆于吾。吾儿学于吾弟。吾弟之文。为侪友所重。而吾弟每称吾儿胜己。若吾儿之行与能。可谓卓绝伦类。使假之年。则是必不但光大我门户而已矣。比我家之祸变相绩。苟吾之罪逆难容。则天何不剿吾命而留吾儿。以承先业继先休。而乃使吾儿至于此。是不惟吾之奇险。实李氏之厄运而门户则亡矣。吾宁不悲欤。吾自遭此悲。尤以莫慰吾母之悲为悲。且吾儿之寡妻稚儿。非吾则谁复存之。吾固忍痛苟活。以至今日。而此悲又何忍忘之耶。惟吾儿之行能。生未能表显于时。殁又泯灭于后。则吾之悲逾益甚。子其有以述之。以纾吾悲。且吾儿长逝之魂。亦可以无恨矣。余哭而对曰。才不才。各言其子。况伯道之才耶。况从舅氏虽不幸困穷。吾知从舅氏之贤。必不私于其子。况伯道之行能。有不待从舅氏之诏之。而余固熟知者耶。苟吾立言。而后之人。惟吾之信焉。则孰复有疑于从舅氏之私耶。然吾畸于世。身方辱贱。宁能张大人而信于后耶。从舅氏又哭而言曰。毋辞。余不敢辞。又不忍辞。遂作辞。辞曰。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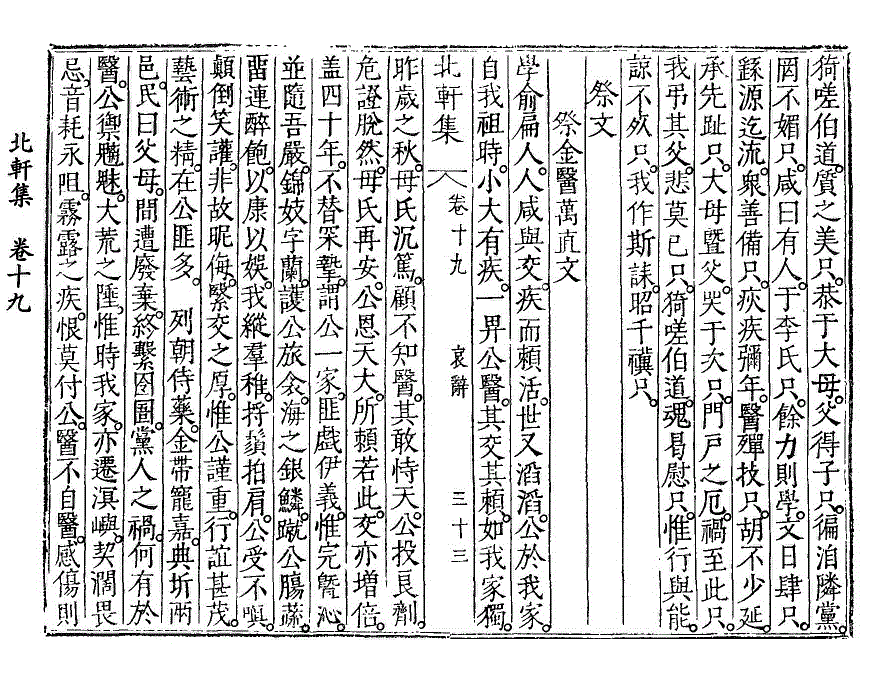 猗嗟伯道。质之美只。恭于大母。父得子只。遍洎邻党。罔不媚只。咸曰有人。于李氏只。馀力则学。文日肆只。繇源迄流。众善备只。疢疾弥年。医殚技只。胡不少延。承先趾只。大母暨父。哭于次只。门户之厄。祸至此只。我吊其父。悲莫已只。猗嗟伯道。魂曷慰只。惟行与能。谅不死只。我作斯诔。昭千𥜥只。
猗嗟伯道。质之美只。恭于大母。父得子只。遍洎邻党。罔不媚只。咸曰有人。于李氏只。馀力则学。文日肆只。繇源迄流。众善备只。疢疾弥年。医殚技只。胡不少延。承先趾只。大母暨父。哭于次只。门户之厄。祸至此只。我吊其父。悲莫已只。猗嗟伯道。魂曷慰只。惟行与能。谅不死只。我作斯诔。昭千𥜥只。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遗录(文)○祭文
祭金医万直文
学俞扁人。人咸与交。疾而赖活。世又滔滔。公于我家。自我祖时。小大有疾。一畀公医。其交其赖。如我家独。昨岁之秋。母氏沉笃。顾不知医。其敢恃天。公投良剂。危證脱然。母氏再安。公恩天大。所赖若此。交亦增倍。盖四十年。不替深挚。谓公一家。匪戏伊义。惟完暨沁。并随吾严。锦妓字兰。护公旅衾。海之银鳞。蹴公肠蔬。留连醉饱。以康以娱。我纵群稚。捋须拍肩。公受不嗔。颠倒笑欢。非故昵侮。繄交之厚。惟公谨重。行谊甚茂。艺术之精。在公匪多。 列朝侍药。金带宠嘉。典圻两邑。民曰父母。间遭废弃。终系囹圄。党人之祸。何有于医。公御魑魅。大荒之陲。惟时我家。亦迁溟屿。契阔畏忌。音耗永阻。雾露之疾。恨莫付公。医不自医。感伤则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九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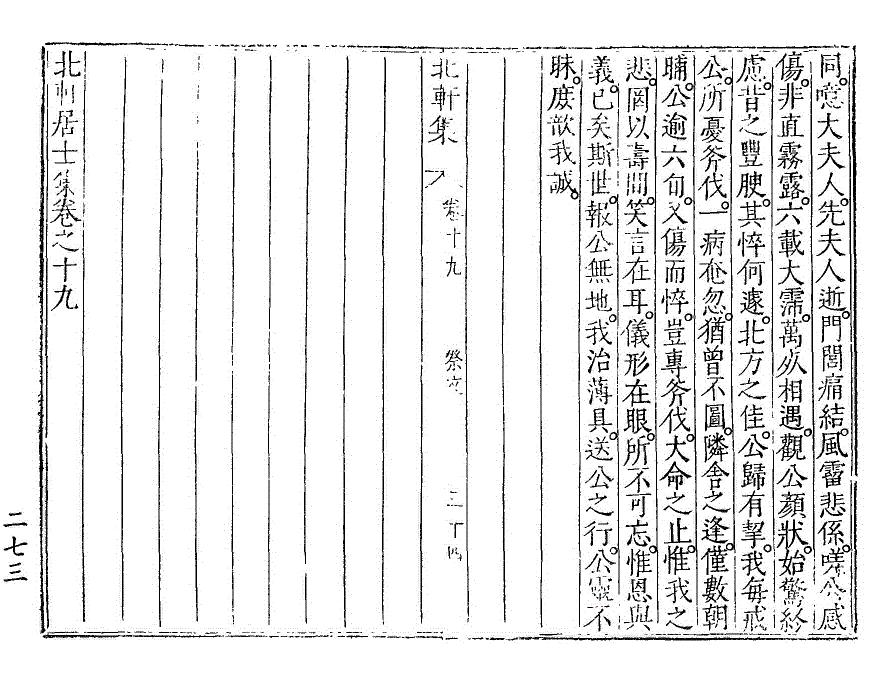 同。噫大夫人。先夫人逝。门闾痛结。风霤悲系。嗟公感伤。非直雾露。六载大霈。万死相遇。观公颜状。始惊终虑。昔之丰腴。其悴何遽。北方之佳。公归有挈。我每戒公。所忧斧伐。一病奄忽。犹曾不图。邻舍之逢。仅数朝晡。公逾六旬。又伤而悴。岂专斧伐。大命之止。惟我之悲。罔以寿间。笑言在耳。仪形在眼。所不可忘。惟恩与义。已矣斯世。报公无地。我治薄具。送公之行。公灵不昧。庶歆我诚。
同。噫大夫人。先夫人逝。门闾痛结。风霤悲系。嗟公感伤。非直雾露。六载大霈。万死相遇。观公颜状。始惊终虑。昔之丰腴。其悴何遽。北方之佳。公归有挈。我每戒公。所忧斧伐。一病奄忽。犹曾不图。邻舍之逢。仅数朝晡。公逾六旬。又伤而悴。岂专斧伐。大命之止。惟我之悲。罔以寿间。笑言在耳。仪形在眼。所不可忘。惟恩与义。已矣斯世。报公无地。我治薄具。送公之行。公灵不昧。庶歆我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