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囚海录(文)○散藁
囚海录(文)○散藁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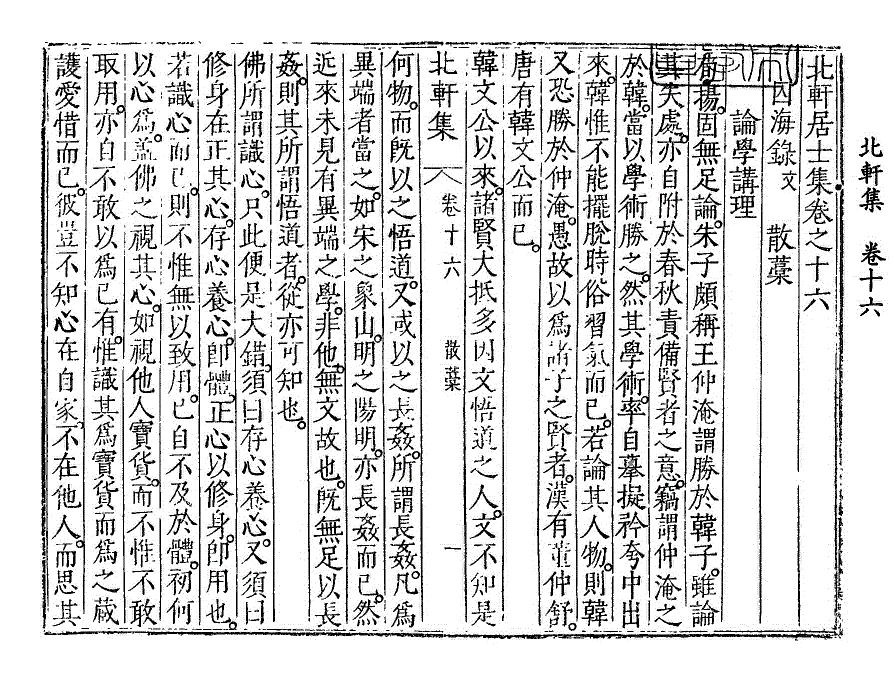 论学讲理
论学讲理荀,扬。固无足论。朱子颇称王仲淹谓胜于韩子。虽论其失处。亦自附于春秋责备贤者之意。窃谓仲淹之于韩。当以学术胜之。然其学术。率自摹拟矜夸中出来。韩惟不能摆脱时俗习气而已。若论其人物。则韩又恐胜于仲淹。愚故以为诸子之贤者。汉有董仲舒。唐有韩文公而已。
韩文公以来。诸贤大抵多因文悟道之人。文不知是何物。而既以之悟道。又或以之长奸。所谓长奸。凡为异端者当之。如宋之象山。明之阳明。亦长奸而已。然近来未见有异端之学。非他。无文故也。既无足以长奸。则其所谓悟道者。从亦可知也。
佛所谓识心。只此便是大错。须曰存心养心。又须曰修身在正其心。存心养心。即体。正心以修身。即用也。若识心而已。则不惟无以致用。已自不及于体。初何以心为。盖佛之视其心。如视他人宝货。而不惟不敢取用。亦自不敢以为己有。惟识其为宝货而为之藏护爱惜而已。彼岂不知心在自家。不在他人。而思其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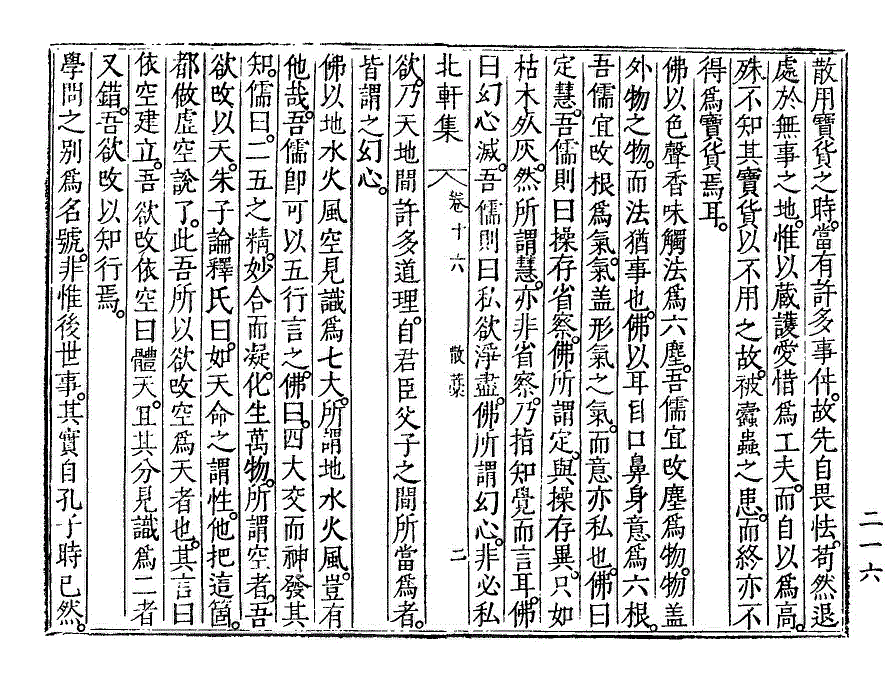 散用宝货之时。当有许多事件。故先自畏怯。苟然退处于无事之地。惟以藏护爱惜为工夫。而自以为高。殊不知其宝货以不用之故。被蠹虫之患。而终亦不得为宝货焉耳。
散用宝货之时。当有许多事件。故先自畏怯。苟然退处于无事之地。惟以藏护爱惜为工夫。而自以为高。殊不知其宝货以不用之故。被蠹虫之患。而终亦不得为宝货焉耳。佛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吾儒宜改尘为物。物盖外物之物。而法犹事也。佛以耳目口鼻身意为六根。吾儒宜改根为气。气盖形气之气。而意亦私也。佛曰定慧。吾儒则曰操存省察。佛所谓定。与操存异。只如枯木死灰。然所谓慧。亦非省察。乃指知觉而言耳。佛曰幻心灭。吾儒则曰私欲净尽。佛所谓幻心。非必私欲。乃天地间许多道理。自君臣父子之间所当为者。皆谓之幻心。
佛以地水火风空见识为七大。所谓地水火风。岂有他哉。吾儒即可以五行言之。佛曰。四大交而神发其知。儒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万物。所谓空者。吾欲改以天。朱子论释氏曰。如天命之谓性。他把这个。都做虚空说了。此吾所以欲改空为天者也。其言曰依空建立。吾欲改依空曰体天。且其分见识为二者又错。吾欲改以知行焉。
学问之别为名号。非惟后世事。其实自孔子时已然。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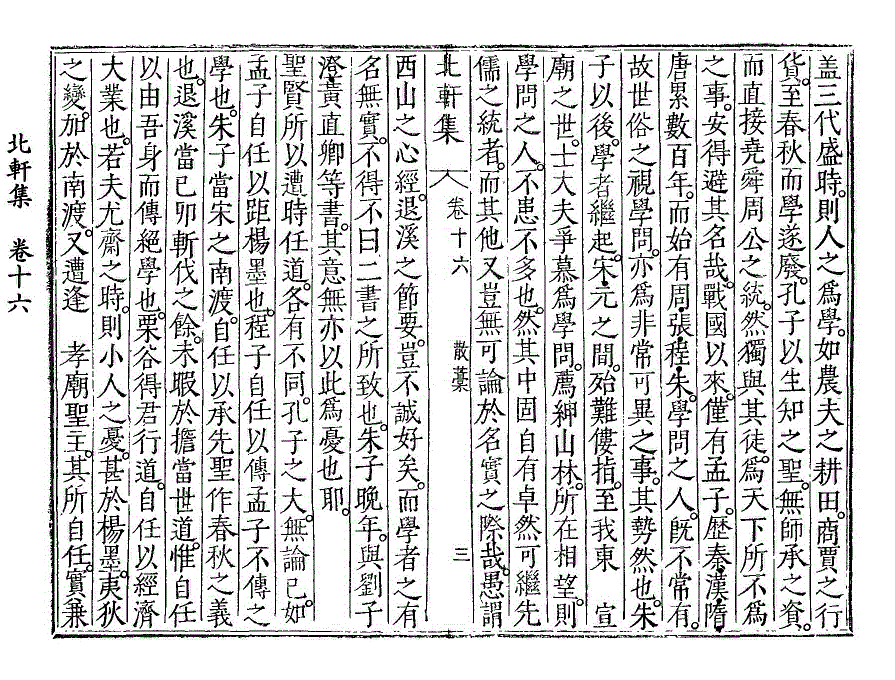 盖三代盛时。则人之为学。如农夫之耕田。商贾之行货。至春秋而学遂废。孔子以生知之圣。无师承之资。而直接尧舜周公之统。然独与其徒。为天下所不为之事。安得避其名哉。战国以来。仅有孟子。历秦,汉,隋,唐累数百年。而始有周,张,程,朱。学问之人。既不常有。故世俗之视学问。亦为非常可异之事。其势然也。朱子以后。学者继起。宋,元之间。殆难偻指。至我东 宣庙之世。士大夫争慕为学问。荐绅山林。所在相望。则学问之人。不患不多也。然其中固自有卓然可继先儒之统者。而其他又岂无可论于名实之际哉。愚谓西山之心经。退溪之节要。岂不诚好矣。而学者之有名无实。不得不曰二书之所致也。朱子晚年。与刘子澄,黄直卿等书。其意无亦以此为忧也耶。
盖三代盛时。则人之为学。如农夫之耕田。商贾之行货。至春秋而学遂废。孔子以生知之圣。无师承之资。而直接尧舜周公之统。然独与其徒。为天下所不为之事。安得避其名哉。战国以来。仅有孟子。历秦,汉,隋,唐累数百年。而始有周,张,程,朱。学问之人。既不常有。故世俗之视学问。亦为非常可异之事。其势然也。朱子以后。学者继起。宋,元之间。殆难偻指。至我东 宣庙之世。士大夫争慕为学问。荐绅山林。所在相望。则学问之人。不患不多也。然其中固自有卓然可继先儒之统者。而其他又岂无可论于名实之际哉。愚谓西山之心经。退溪之节要。岂不诚好矣。而学者之有名无实。不得不曰二书之所致也。朱子晚年。与刘子澄,黄直卿等书。其意无亦以此为忧也耶。圣贤所以遭时任道。各有不同。孔子之大。无论已。如孟子自任以距杨墨也。程子自任以传孟子不传之学也。朱子当宋之南渡。自任以承先圣作春秋之义也。退溪当己卯斩伐之馀。未暇于担当世道。惟自任以由吾身而传绝学也。栗谷得君行道。自任以经济大业也。若夫尤斋之时。则小人之忧。甚于杨墨。夷狄之变。加于南渡。又遭逢 孝庙圣主。其所自任。实兼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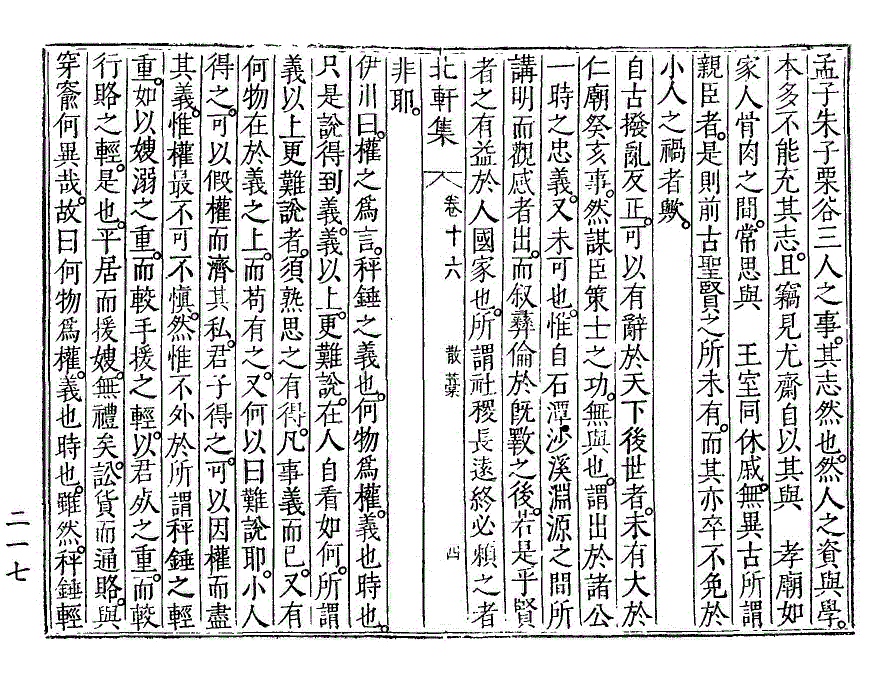 孟子朱子栗谷三人之事。其志然也。然人之资与学。本多不能充其志。且窃见尤斋自以其与 孝庙如家人骨肉之间。常思与 王室同休戚。无异古所谓亲臣者。是则前古圣贤之所未有。而其亦卒不免于小人之祸者欤。
孟子朱子栗谷三人之事。其志然也。然人之资与学。本多不能充其志。且窃见尤斋自以其与 孝庙如家人骨肉之间。常思与 王室同休戚。无异古所谓亲臣者。是则前古圣贤之所未有。而其亦卒不免于小人之祸者欤。自古拨乱反正。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者。未有大于仁庙癸亥事。然谋臣策士之功。无与也。谓出于诸公一时之忠义。又未可也。惟自石潭,沙溪渊源之间所讲明而观感者出。而叙彝伦于既斁之后。若是乎贤者之有益于人国家也。所谓社稷长远终必赖之者非耶。
伊川曰。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所谓义以上更难说者。须熟思之有得。凡事义而已。又有何物在于义之上。而苟有之。又何以曰难说耶。小人得之。可以假权而济其私。君子得之。可以因权而尽其义。惟权最不可不慎。然惟不外于所谓秤锤之轻重。如以嫂溺之重。而较手援之轻。以君死之重。而较行赂之轻。是也。平居而援嫂。无礼矣。讼货而通赂。与穿窬何异哉。故曰何物为权。义也时也。虽然。秤锤轻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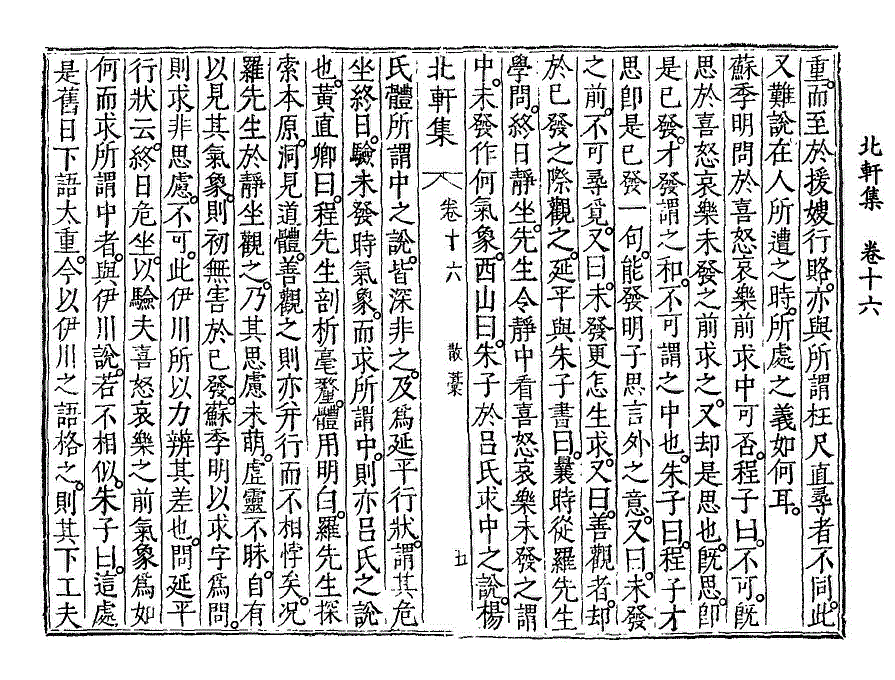 重。而至于援嫂行赂。亦与所谓枉尺直寻者不同。此又难说。在人所遭之时。所处之义如何耳。
重。而至于援嫂行赂。亦与所谓枉尺直寻者不同。此又难说。在人所遭之时。所处之义如何耳。苏季明问于喜怒哀乐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发一句。能发明子思言外之意。又曰。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又曰。未发更怎生求。又曰。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延平与朱子书曰。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静坐。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作何气象。西山曰。朱子于吕氏求中之说。杨氏体所谓中之说。皆深非之。及为延平行状。谓其危坐终日。验未发时气象。而求所谓中。则亦吕氏之说也。黄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体用明白。罗先生探索本原。洞见道体。善观之则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况罗先生于静坐观之。乃其思虑未萌。虚灵不昧。自有以见其气象。则初无害于已发。苏季明以求字为问。则求非思虑。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问延平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说。若不相似。朱子曰。这处是旧日下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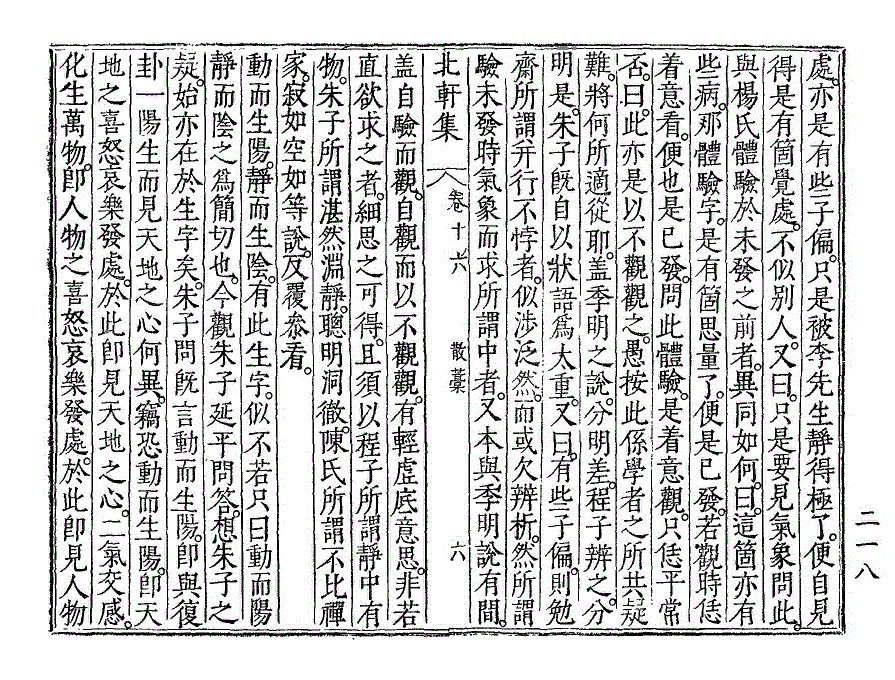 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又曰。只是要见气象问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愚按此系学者之所共疑难。将何所适从耶。盖季明之说。分明差。程子辨之。分明是。朱子既自以状语为太重。又曰。有些子偏。则勉斋所谓并行不悖者。似涉泛然。而或欠辨析。然所谓验未发时气象而求所谓中者。又本与季明说有间。盖自验而观。自观而以不观观。有轻虚底意思。非若直欲求之者。细思之可得。且须以程子所谓静中有物。朱子所谓湛然渊静。聪明洞彻。陈氏所谓不比禅家。寂如空如等说。反覆参看。
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又曰。只是要见气象问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愚按此系学者之所共疑难。将何所适从耶。盖季明之说。分明差。程子辨之。分明是。朱子既自以状语为太重。又曰。有些子偏。则勉斋所谓并行不悖者。似涉泛然。而或欠辨析。然所谓验未发时气象而求所谓中者。又本与季明说有间。盖自验而观。自观而以不观观。有轻虚底意思。非若直欲求之者。细思之可得。且须以程子所谓静中有物。朱子所谓湛然渊静。聪明洞彻。陈氏所谓不比禅家。寂如空如等说。反覆参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有此生字。似不若只曰动而阳静而阴之为简切也。今观朱子延平问答。想朱子之疑。始亦在于生字矣。朱子问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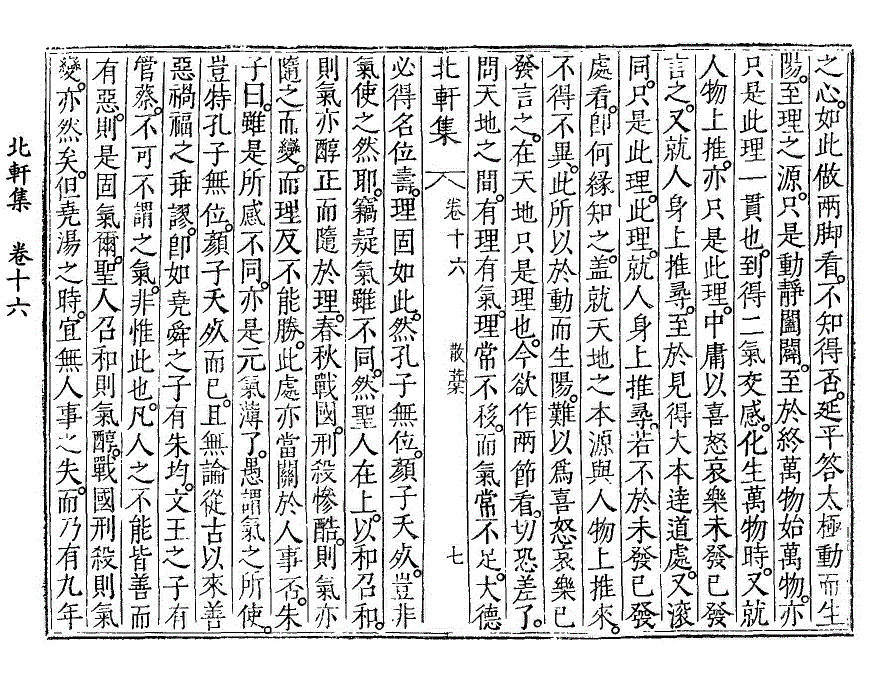 之心。如此做两脚看。不知得否。延平答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滚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以为喜怒哀乐已发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两节看。切恐差了。问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常不移。而气常不足。大德必得名位寿。理固如此。然孔子无位。颜子夭死。岂非气使之然耶。窃疑气虽不同。然圣人在上。以和召和。则气亦醇正而随于理。春秋战国。刑杀惨酷。则气亦随之而变。而理反不能胜。此处亦当关于人事否。朱子曰。虽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气薄了。愚谓气之所使。岂特孔子无位。颜子夭死而已。且无论从古以来善恶祸福之乖谬。即如尧舜之子有朱均。文王之子有管蔡。不可不谓之气。非惟此也。凡人之不能皆善而有恶。则是固气尔。圣人召和则气醇。战国刑杀则气变。亦然矣。但尧汤之时。宜无人事之失。而乃有九年
之心。如此做两脚看。不知得否。延平答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滚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以为喜怒哀乐已发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两节看。切恐差了。问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常不移。而气常不足。大德必得名位寿。理固如此。然孔子无位。颜子夭死。岂非气使之然耶。窃疑气虽不同。然圣人在上。以和召和。则气亦醇正而随于理。春秋战国。刑杀惨酷。则气亦随之而变。而理反不能胜。此处亦当关于人事否。朱子曰。虽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气薄了。愚谓气之所使。岂特孔子无位。颜子夭死而已。且无论从古以来善恶祸福之乖谬。即如尧舜之子有朱均。文王之子有管蔡。不可不谓之气。非惟此也。凡人之不能皆善而有恶。则是固气尔。圣人召和则气醇。战国刑杀则气变。亦然矣。但尧汤之时。宜无人事之失。而乃有九年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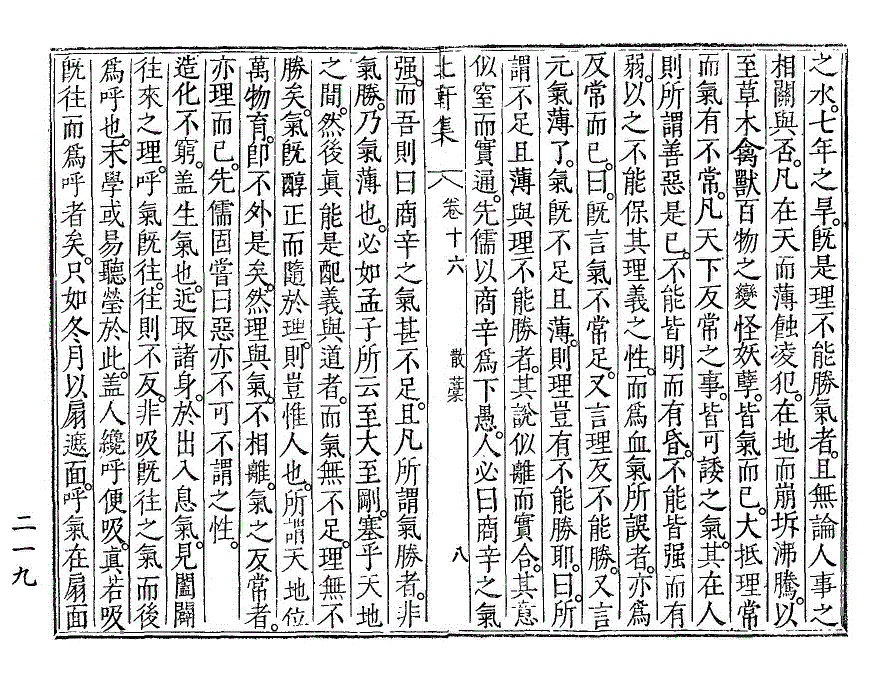 之水。七年之旱。既是理不能胜气者。且无论人事之相关与否。凡在天而薄蚀凌犯。在地而崩坼沸腾。以至草木禽兽百物之变怪妖孽。皆气而已。大抵理常而气有不常。凡天下反常之事。皆可诿之气。其在人则所谓善恶是已。不能皆明而有昏。不能皆强而有弱。以之不能保其理义之性。而为血气所误者。亦为反常而已。曰。既言气不常足。又言理反不能胜。又言元气薄了。气既不足且薄。则理岂有不能胜耶。曰。所谓不足且薄与理不能胜者。其说似离而实合。其意似窒而实通。先儒以商辛为下愚。人必曰商辛之气强。而吾则曰商辛之气甚不足。且凡所谓气胜者。非气胜。乃气薄也。必如孟子所云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然后真能是配义与道者。而气无不足。理无不胜矣。气既醇正而随于理。则岂惟人也。所谓天地位万物育。即不外是矣。然理与气。不相离。气之反常者。亦理而已。先儒固尝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之水。七年之旱。既是理不能胜气者。且无论人事之相关与否。凡在天而薄蚀凌犯。在地而崩坼沸腾。以至草木禽兽百物之变怪妖孽。皆气而已。大抵理常而气有不常。凡天下反常之事。皆可诿之气。其在人则所谓善恶是已。不能皆明而有昏。不能皆强而有弱。以之不能保其理义之性。而为血气所误者。亦为反常而已。曰。既言气不常足。又言理反不能胜。又言元气薄了。气既不足且薄。则理岂有不能胜耶。曰。所谓不足且薄与理不能胜者。其说似离而实合。其意似窒而实通。先儒以商辛为下愚。人必曰商辛之气强。而吾则曰商辛之气甚不足。且凡所谓气胜者。非气胜。乃气薄也。必如孟子所云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然后真能是配义与道者。而气无不足。理无不胜矣。气既醇正而随于理。则岂惟人也。所谓天地位万物育。即不外是矣。然理与气。不相离。气之反常者。亦理而已。先儒固尝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造化不穷。盖生气也。近取诸身。于出入息气。见阖辟往来之理。呼气既往。往则不反。非吸既往之气而后为呼也。末学或易听莹于此。盖人才呼便吸。真若吸既往而为呼者矣。只如冬月以扇遮面。呼气在扇面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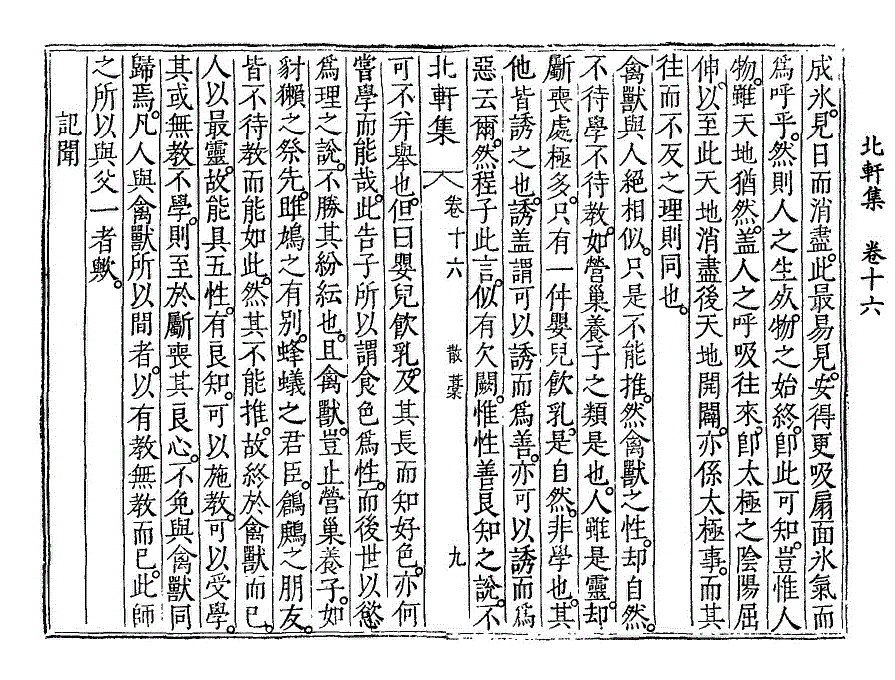 成冰。见日而消尽。此最易见。安得更吸扇面冰气而为呼乎。然则人之生死。物之始终。即此可知。岂惟人物。虽天地犹然。盖人之呼吸往来。即太极之阴阳屈伸。以至此天地消尽后天地开辟。亦系太极事。而其往而不反之理则同也。
成冰。见日而消尽。此最易见。安得更吸扇面冰气而为呼乎。然则人之生死。物之始终。即此可知。岂惟人物。虽天地犹然。盖人之呼吸往来。即太极之阴阳屈伸。以至此天地消尽后天地开辟。亦系太极事。而其往而不反之理则同也。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待学不待教。如营巢养子之类是也。人虽是灵。却斸丧处极多。只有一件婴儿饮乳。是自然。非学也。其他皆诱之也。诱盖谓可以诱而为善。亦可以诱而为恶云尔。然程子此言。似有欠阙。惟性善良知之说。不可不并举也。但曰婴儿饮乳。及其长而知好色。亦何尝学而能哉。此告子所以谓食色为性。而后世以欲为理之说。不胜其纷纭也。且禽兽。岂止营巢养子。如豺獭之祭先。雎鸠之有别。蜂蚁之君臣。鸧鹒之朋友。皆不待教而能如此。然其不能推。故终于禽兽而已。人以最灵。故能具五性。有良知。可以施教。可以受学。其或无教不学。则至于斸丧其良心。不免与禽兽同归焉。凡人与禽兽所以间者。以有教无教而已。此师之所以与父一者欤。
记闻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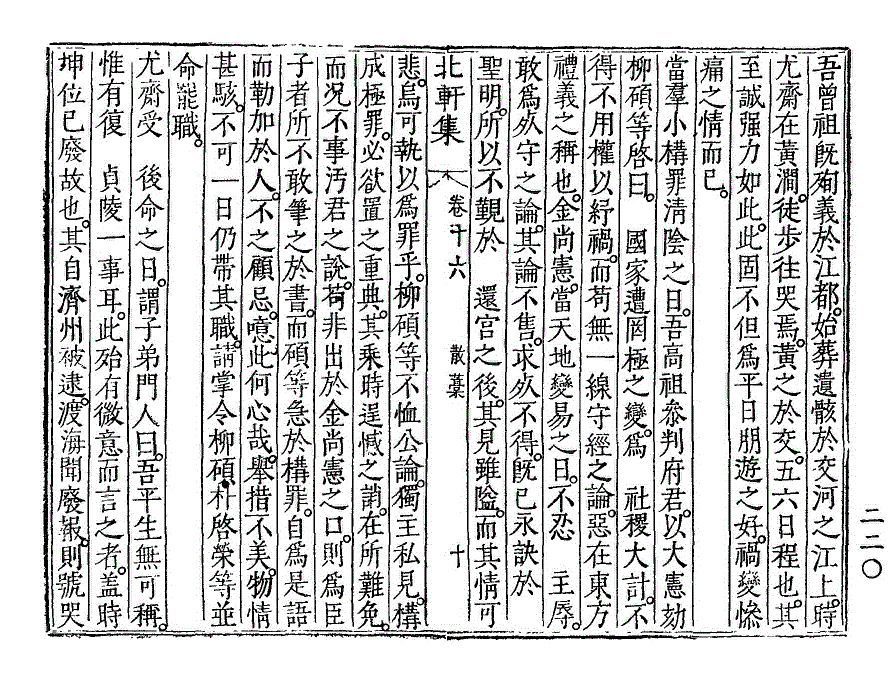 吾曾祖既殉义于江都。始葬遗骸于交河之江上。时尤斋在黄涧。徒步往哭焉。黄之于交。五六日程也。其至诚强力如此。此固不但为平日朋游之好。祸变惨痛之情而已。
吾曾祖既殉义于江都。始葬遗骸于交河之江上。时尤斋在黄涧。徒步往哭焉。黄之于交。五六日程也。其至诚强力如此。此固不但为平日朋游之好。祸变惨痛之情而已。当群小构罪清阴之日。吾高祖参判府君。以大宪劾柳硕等启曰。 国家遭罔极之变。为 社稷大计。不得不用权以纾祸。而苟无一线守经之论。恶在东方礼义之称也。金尚宪。当天地变易之日。不忍 主辱。敢为死守之论。其论不售。求死不得。既已永诀于 圣明。所以不觐于 还宫之后。其见虽隘。而其情可悲。乌可执以为罪乎。柳硕等不恤公论。独主私见。构成极罪。必欲置之重典。其乘时逞憾之诮。在所难免。而况不事污君之说。苟非出于金尚宪之口。则为臣子者所不敢笔之于书。而硕等急于构罪。自为是语而勒加于人。不之顾忌。噫。此何心哉。举措不美。物情甚骇。不可一日仍带其职。请掌令柳硕,朴启荣等并命罢职。
尤斋受 后命之日。谓子弟门人曰。吾平生无可称。惟有复 贞陵一事耳。此殆有微意而言之者。盖时坤位已废故也。其自济州被逮。渡海闻废报。则号哭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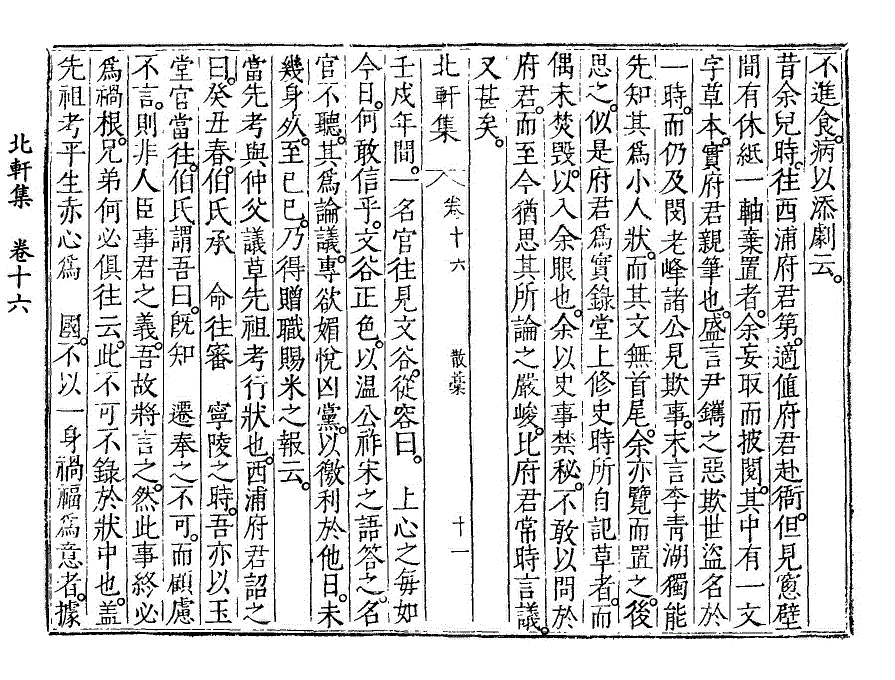 不进食。病以添剧云。
不进食。病以添剧云。昔余儿时。往西浦府君第。适值府君赴衙。但见窗壁间有休纸一轴弃置者。余妄取而披阅。其中有一文字草本。实府君亲笔也。盛言尹镌(一作鑴)之恶欺世盗名于一时。而仍及闵老峰诸公见欺事。末言李青湖独能先知其为小人状。而其文无首尾。余亦览而置之。后思之。似是府君为实录堂上修史时所自记草者。而偶未焚毁。以入余眼也。余以史事禁秘。不敢以问于府君。而至今犹思其所论之严峻。比府君常时言议。又甚矣。
壬戌年间。一名官往见文谷。从容曰。 上心之每如今日。何敢信乎。文谷正色。以温公祚宋之语答之。名官不听。其为论议。专欲媚悦凶党。以徼利于他日。未几身死。至己巳。乃得赠职赐米之报云。
当先考与仲父议草先祖考行状也。西浦府君诏之曰。癸丑春。伯氏承 命往审 宁陵之时。吾亦以玉堂官当往。伯氏谓吾曰。既知 迁奉之不可。而顾虑不言。则非人臣事君之义。吾故将言之。然此事终必为祸根。兄弟何必俱往云。此不可不录于状中也。盖先祖考平生赤心为 国。不以一身祸福为意者。据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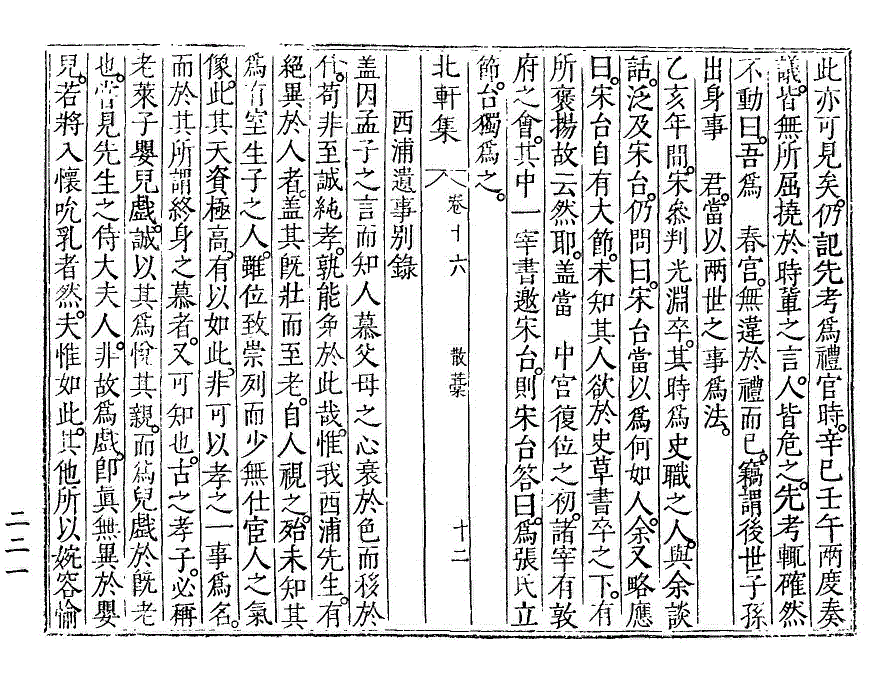 此亦可见矣。仍记先考为礼官时。辛巳壬午两度奏议。皆无所屈挠于时辈之言。人皆危之。先考辄确然不动曰。吾为 春宫。无违于礼而已。窃谓后世子孙出身事 君。当以两世之事为法。
此亦可见矣。仍记先考为礼官时。辛巳壬午两度奏议。皆无所屈挠于时辈之言。人皆危之。先考辄确然不动曰。吾为 春宫。无违于礼而已。窃谓后世子孙出身事 君。当以两世之事为法。乙亥年间。宋参判光渊卒。其时为史职之人。与余谈话。泛及宋台。仍问曰。宋台当以为何如人。余又略应曰。宋台自有大节。未知其人欲于史草书卒之下。有所褒扬故云然耶。盖当 中宫复位之初。诸宰有敦府之会。其中一宰书邀宋台。则宋台答曰。为张氏立节。台独为之。
西浦遗事别录
盖因孟子之言而知人慕父母之心衰于色而移于仕。苟非至诚纯孝。孰能免于此哉。惟我西浦先生。有绝异于人者。盖其既壮而至老。自人视之。殆未知其为有室生子之人。虽位致崇列而少无仕宦人之气像。此其天资极高。有以如此。非可以孝之一事为名。而于其所谓终身之慕者。又可知也。古之孝子。必称老莱子婴儿戏。诚以其为悦其亲。而为儿戏于既老也。尝见先生之侍大夫人。非故为戏。即真无异于婴儿。若将入怀吮乳者然。夫惟如此。其他所以婉容愉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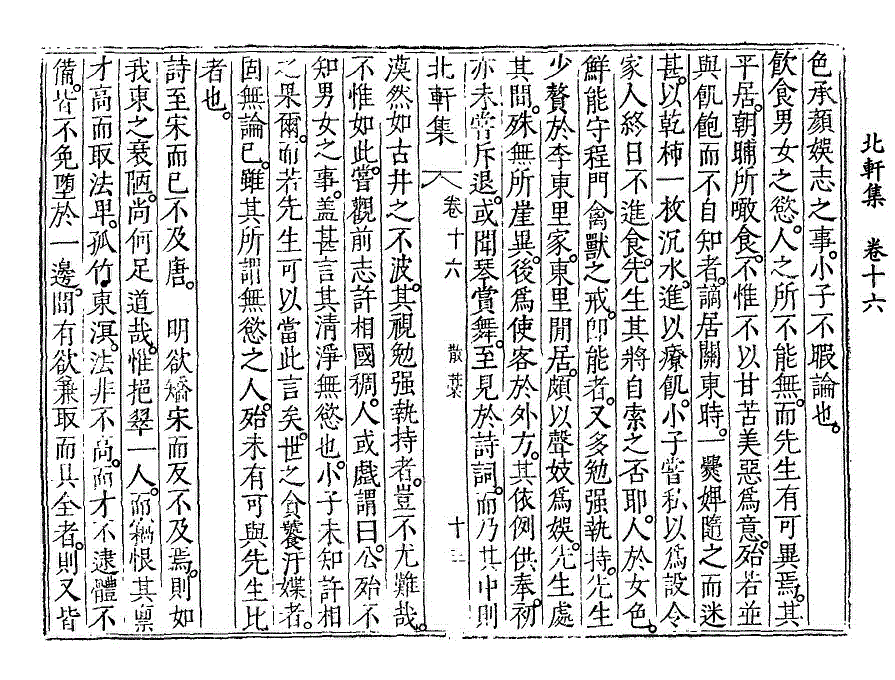 色承颜娱志之事。小子不暇论也。
色承颜娱志之事。小子不暇论也。饮食男女之欲。人之所不能无。而先生有可异焉。其平居。朝晡所啖食。不惟不以甘苦美恶为意。殆若并与饥饱而不自知者。谪居关东时。一爨婢随之而迷甚。以乾柿一枚沉水。进以疗饥。小子尝私以为设令家人终日不进食。先生其将自索之否耶。人于女色。鲜能守程门禽兽之戒。即能者。又多勉强执持。先生少赘于李东里家。东里閒居。颇以声妓为娱。先生处其间。殊无所崖异。后为使客于外方。其依例供奉。初亦未尝斥退。或闻琴赏舞。至见于诗词。而乃其中则漠然如古井之不波。其视勉强执持者。岂不尤难哉。不惟如此。尝观前志许相国稠。人或戏谓曰。公殆不知男女之事。盖甚言其清净无欲也。小子未知许相之果尔。而若先生可以当此言矣。世之贪饕污媟者。固无论已。虽其所谓无欲之人。殆未有可与先生比者也。
诗至宋而已不及唐。 明欲矫宋而反不及焉。则如我东之衰陋。尚何足道哉。惟挹翠一人。而窃恨其禀才高而取法卑。孤竹,东溟。法非不高。而才不逮体不备。皆不免堕于一边。间有欲兼取而具全者。则又皆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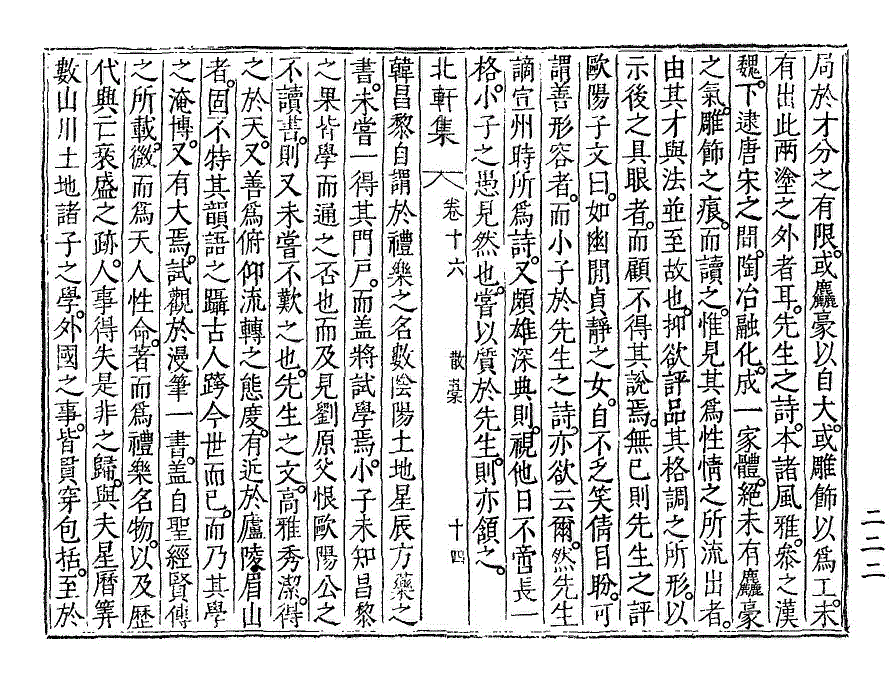 局于才分之有限。或粗豪以自大。或雕饰以为工。未有出此两涂之外者耳。先生之诗。本诸风雅。参之汉魏。下逮唐宋之间。陶冶融化。成一家体。绝未有粗豪之气。雕饰之痕。而读之。惟见其为性情之所流出者。由其才与法并至故也。抑欲评品其格调之所形。以示后之具眼者。而顾不得其说焉。无已则先生之评欧阳子文曰。如幽閒贞静之女。自不乏笑倩目盼。可谓善形容者。而小子于先生之诗。亦欲云尔。然先生谪宣州时所为诗。又颇雄深典则。视他日不啻长一格。小子之愚见然也。尝以质于先生。则亦颔之。
局于才分之有限。或粗豪以自大。或雕饰以为工。未有出此两涂之外者耳。先生之诗。本诸风雅。参之汉魏。下逮唐宋之间。陶冶融化。成一家体。绝未有粗豪之气。雕饰之痕。而读之。惟见其为性情之所流出者。由其才与法并至故也。抑欲评品其格调之所形。以示后之具眼者。而顾不得其说焉。无已则先生之评欧阳子文曰。如幽閒贞静之女。自不乏笑倩目盼。可谓善形容者。而小子于先生之诗。亦欲云尔。然先生谪宣州时所为诗。又颇雄深典则。视他日不啻长一格。小子之愚见然也。尝以质于先生。则亦颔之。韩昌黎自谓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而盖将试学焉。小子未知昌黎之果皆学而通之否也而及见刘原父恨欧阳公之不读书。则又未尝不叹之也。先生之文。高雅秀洁。得之于天。又善为俯仰流转之态度。有近于庐陵,眉山者。固不特其韵语之蹑古人跨今世而已。而乃其学之淹博。又有大焉。试观于漫笔一书。盖自圣经贤传之所载。微而为天人性命。著而为礼乐名物。以及历代兴亡衰盛之迹。人事得失是非之归。与夫星历算数山川土地诸子之学。外国之事。皆贯穿包括。至于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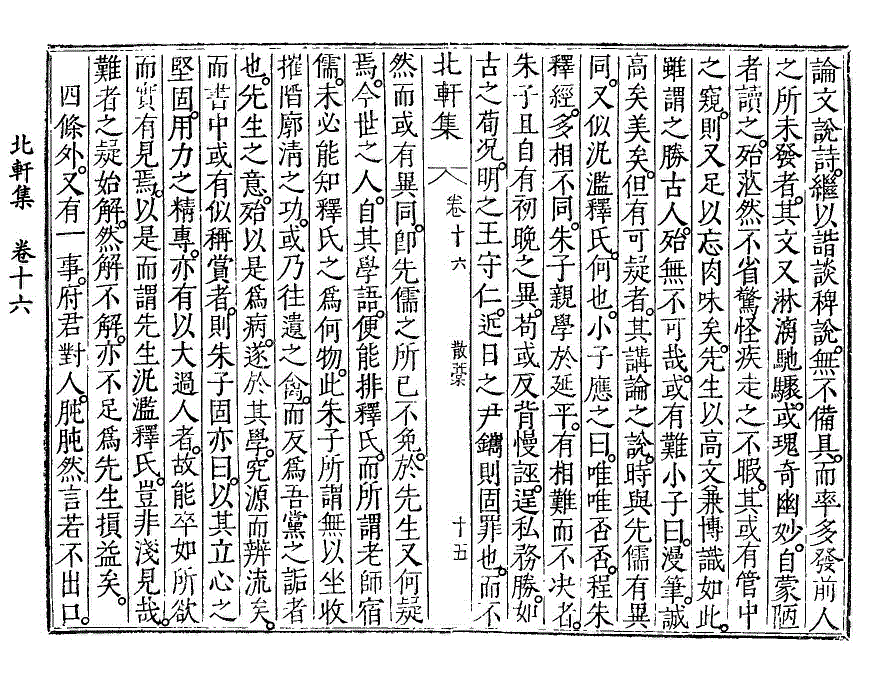 论文说诗。继以谐谈稗说。无不备具。而率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者。其文又淋漓驰骤。或瑰奇幽妙。自蒙陋者读之。殆茫然不省惊怪疾走之不暇。其或有管中之窥。则又足以忘肉味矣。先生以高文兼博识如此。虽谓之胜古人。殆无不可哉。或有难小子曰。漫笔。诚高矣美矣。但有可疑者。其讲论之说。时与先儒有异同。又似汎滥释氏。何也。小子应之曰。唯唯否否。程朱释经。多相不同。朱子亲学于延平。有相难而不决者。朱子且自有初晚之异。苟或反背慢诬。逞私务胜。如古之荀况。明之王守仁。近日之尹镌(一作鑴)则固罪也。而不然而或有异同。即先儒之所已不免。于先生又何疑焉。今世之人。自其学语。便能排释氏。而所谓老师宿儒。未必能知释氏之为何物。此朱子所谓无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遗之禽。而反为吾党之诟者也。先生之意。殆以是为病。遂于其学。究源而辨流矣。而书中或有似称赏者。则朱子固亦曰。以其立心之坚固。用力之精专。亦有以大过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实有见焉。以是而谓先生汎滥释氏。岂非浅见哉。难者之疑始解。然解不解。亦不足为先生损益矣。
论文说诗。继以谐谈稗说。无不备具。而率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者。其文又淋漓驰骤。或瑰奇幽妙。自蒙陋者读之。殆茫然不省惊怪疾走之不暇。其或有管中之窥。则又足以忘肉味矣。先生以高文兼博识如此。虽谓之胜古人。殆无不可哉。或有难小子曰。漫笔。诚高矣美矣。但有可疑者。其讲论之说。时与先儒有异同。又似汎滥释氏。何也。小子应之曰。唯唯否否。程朱释经。多相不同。朱子亲学于延平。有相难而不决者。朱子且自有初晚之异。苟或反背慢诬。逞私务胜。如古之荀况。明之王守仁。近日之尹镌(一作鑴)则固罪也。而不然而或有异同。即先儒之所已不免。于先生又何疑焉。今世之人。自其学语。便能排释氏。而所谓老师宿儒。未必能知释氏之为何物。此朱子所谓无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遗之禽。而反为吾党之诟者也。先生之意。殆以是为病。遂于其学。究源而辨流矣。而书中或有似称赏者。则朱子固亦曰。以其立心之坚固。用力之精专。亦有以大过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实有见焉。以是而谓先生汎滥释氏。岂非浅见哉。难者之疑始解。然解不解。亦不足为先生损益矣。四条外。又有一事。府君对人。肫肫然言若不出口。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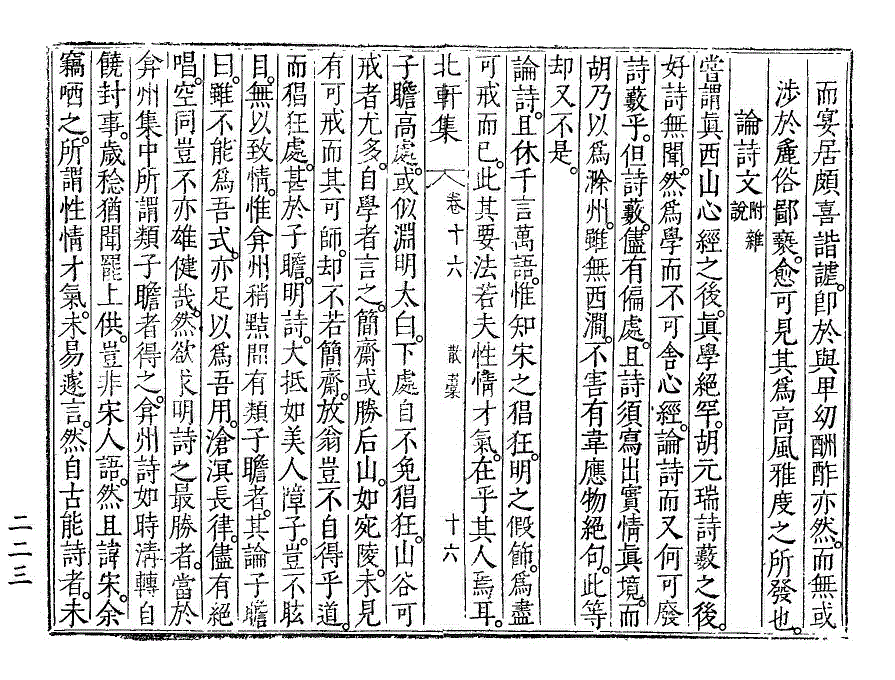 而宴居颇喜谐谑。即于与卑幼酬酢亦然。而无或涉于粗俗鄙亵。愈可见其为高风雅度之所发也。
而宴居颇喜谐谑。即于与卑幼酬酢亦然。而无或涉于粗俗鄙亵。愈可见其为高风雅度之所发也。论诗文(附杂说)
尝谓真西山心经之后。真学绝罕。胡元瑞诗薮之后。好诗无闻。然为学而不可舍心经。论诗而又何可废诗薮乎。但诗薮。尽有偏处。且诗须写出实情真境。而胡乃以为滁州。虽无西涧。不害有韦应物绝句。此等却又不是。
论诗。且休千言万语。惟知宋之猖狂。明之假饰。为尽可戒而已。此其要法若夫性情才气。在乎其人焉耳。子瞻高处。或似渊明太白。下处自不免猖狂。山谷可戒者尤多。自学者言之。简斋或胜后山。如宛陵。未见有可戒而其可师。却不若简斋。放翁岂不自得乎道。而猖狂处。甚于子瞻。明诗。大抵如美人障子。岂不眩目。无以致情。惟弇州稍黠间有类子瞻者。其论子瞻曰。虽不能为吾式。亦足以为吾用。沧溟长律。尽有绝唱。空同岂不亦雄健哉。然欲求明诗之最胜者。当于弇州集中所谓类子瞻者得之。弇州诗如时清转自饶封事。岁稔犹闻罢上供。岂非宋人语。然且讳宋。余窃哂之。所谓性情才气。未易遽言。然自古能诗者。未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4H 页
 必皆高人达士。或多奸雄浪子。而惟庸俗之人。鲜有能诗。
必皆高人达士。或多奸雄浪子。而惟庸俗之人。鲜有能诗。言语文字。实有古今之异。亦不系其人之贤否。古人曰。暮春者。春服既成。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尝曰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閒学少年。古人曰。百尔君子。不知德行。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尝曰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古人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何尝曰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古人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曰。对酒当歌。又曰。远望可以当归。何尝曰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然所谓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所谓明朝试捲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尽好。如感兴诗。唐宋以来。殆未或见。
东方之诗。翠轩为最。但以其少时所作。或病粗率。使假之年。当胜东坡。其才然也。然余恨其取法不高。或有自以谓法高者。才又不逮。如苏斋。终日矻矻于绳墨之间。而似不知九方皋相马之术者。东溟。其亦杰出矣。而要不出明人轨度耳。其他又鲜有可观。吾家西浦翁。古诗短律。本诸风雅。出入骚选唐宋。多有绝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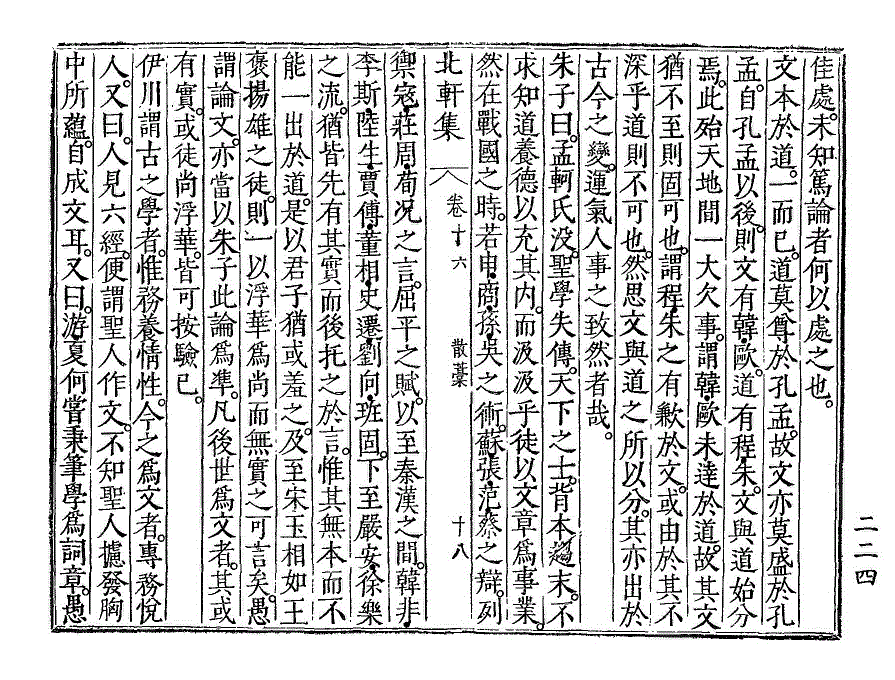 佳处。未知笃论者何以处之也。
佳处。未知笃论者何以处之也。文本于道。一而已。道莫尊于孔孟。故文亦莫盛于孔孟。自孔孟以后。则文有韩,欧。道有程,朱。文与道始分焉。此殆天地间一大欠事。谓韩,欧未达于道。故其文犹不至则固可也。谓程,朱之有歉于文。或由于其不深乎道则不可也。然思文与道之所以分。其亦出于古今之变。运气人事之致然者哉。
朱子曰。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傅,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惟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愚谓论文。亦当以朱子此论为准。凡后世为文者。其或有实。或徒尚浮华。皆可按验已。
伊川谓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今之为文者。专务悦人。又曰。人见六经。便谓圣人作文。不知圣人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又曰。游,夏何尝秉笔学为词章。愚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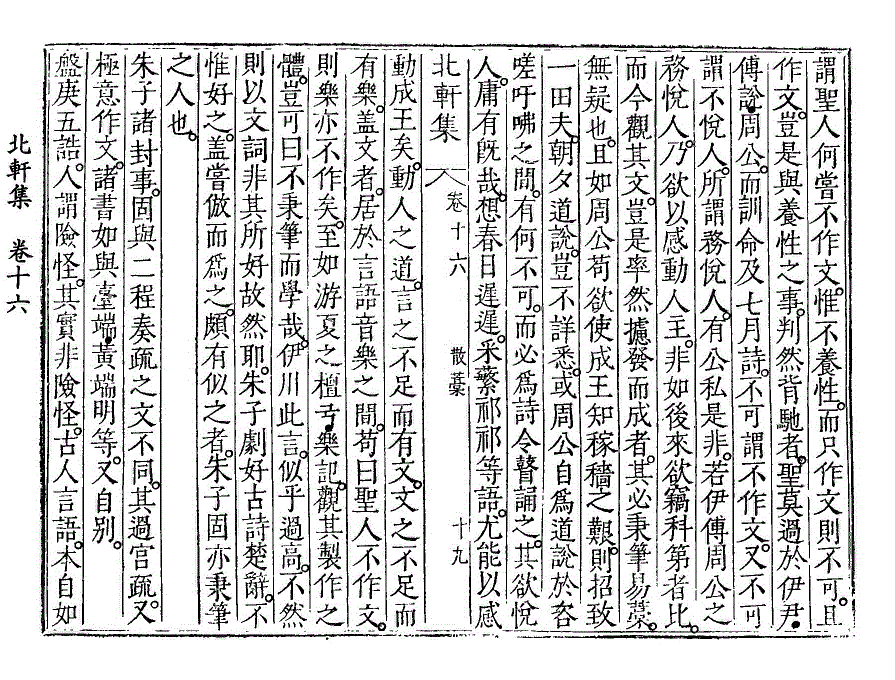 谓圣人何尝不作文。惟不养性。而只作文则不可。且作文。岂是与养性之事。判然背驰者。圣莫过于伊尹,傅说,周公。而训命及七月诗。不可谓不作文。又不可谓不悦人。所谓务悦人。有公私是非。若伊傅周公之务悦人。乃欲以感动人主。非如后来欲窃科第者比。而今观其文。岂是率然摅发而成者。其必秉笔易藁。无疑也。且如周公苟欲使成王知稼穑之艰。则招致一田夫。朝夕道说。岂不详悉。或周公自为道说于咨嗟吁咈之间。有何不可。而必为诗令瞽诵之。其欲悦人。庸有既哉。想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等语。尤能以感动成王矣。动人之道。言之不足而有文。文之不足而有乐。盖文者。居于言语音乐之间。苟曰圣人不作文。则乐亦不作矣。至如游夏之檀弓,乐记。观其制作之体。岂可曰不秉笔而学哉。伊川此言。似乎过高。不然则以文词非其所好故然耶。朱子剧好古诗楚辞。不惟好之。盖尝仿而为之。颇有似之者。朱子固亦秉笔之人也。
谓圣人何尝不作文。惟不养性。而只作文则不可。且作文。岂是与养性之事。判然背驰者。圣莫过于伊尹,傅说,周公。而训命及七月诗。不可谓不作文。又不可谓不悦人。所谓务悦人。有公私是非。若伊傅周公之务悦人。乃欲以感动人主。非如后来欲窃科第者比。而今观其文。岂是率然摅发而成者。其必秉笔易藁。无疑也。且如周公苟欲使成王知稼穑之艰。则招致一田夫。朝夕道说。岂不详悉。或周公自为道说于咨嗟吁咈之间。有何不可。而必为诗令瞽诵之。其欲悦人。庸有既哉。想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等语。尤能以感动成王矣。动人之道。言之不足而有文。文之不足而有乐。盖文者。居于言语音乐之间。苟曰圣人不作文。则乐亦不作矣。至如游夏之檀弓,乐记。观其制作之体。岂可曰不秉笔而学哉。伊川此言。似乎过高。不然则以文词非其所好故然耶。朱子剧好古诗楚辞。不惟好之。盖尝仿而为之。颇有似之者。朱子固亦秉笔之人也。朱子诸封事。固与二程奏疏之文不同。其过宫疏。又极意作文。诸书如与台端,黄端明等。又自别。
盘庚五诰。人谓险怪。其实非险怪。古人言语。本自如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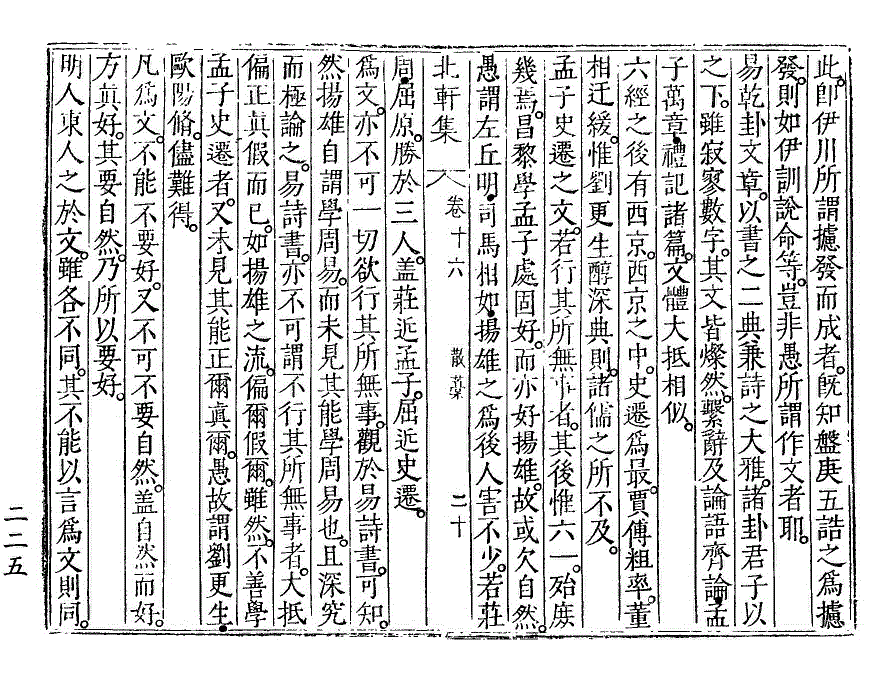 此。即伊川所谓摅发而成者。既知盘庚五诰之为摅发。则如伊训说命等。岂非愚所谓作文者耶。
此。即伊川所谓摅发而成者。既知盘庚五诰之为摅发。则如伊训说命等。岂非愚所谓作文者耶。易乾卦文章。以书之二典兼诗之大雅。诸卦君子以之下。虽寂寥数字。其文皆灿然。系辞及论语齐论,孟子万章,礼记诸篇。文体大抵相似。
六经之后有西京。西京之中。史迁为最。贾傅粗率。董相迂缓。惟刘更生醇深典则。诸儒之所不及。
孟子史迁之文。若行其所无事者。其后惟六一。殆庶几焉。昌黎学孟子处固好。而亦好扬雄。故或欠自然。愚谓左丘明,司马相如,扬雄之为后人害不少。若庄周,屈原。胜于三人。盖庄近孟子。屈近史迁。
为文。亦不可一切欲行其所无事。观于易诗书。可知。然扬雄自谓学周易。而未见其能学周易也。且深究而极论之。易诗书。亦不可谓不行其所无事者。大抵偏正真假而已。如扬雄之流。偏尔假尔。虽然。不善学孟子史迁者。又未见其能正尔真尔。愚故谓刘更生,欧阳脩。尽难得。
凡为文。不能不要好。又不可不要自然。盖自然而好。方真好。其要自然。乃所以要好。
明人东人之于文。虽各不同。其不能以言为文则同。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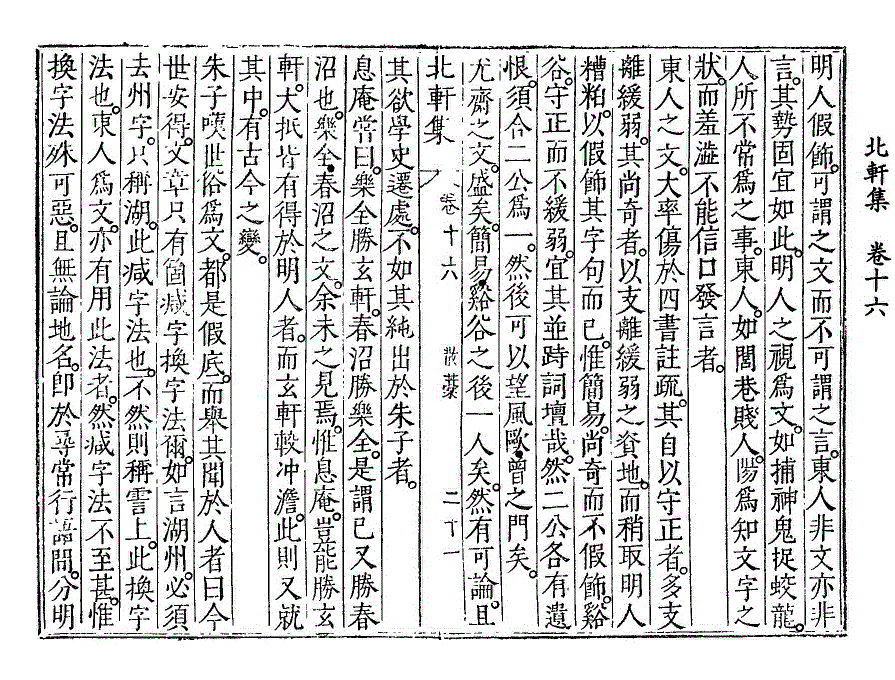 明人假饰。可谓之文而不可谓之言。东人非文亦非言。其势固宜如此。明人之视为文。如捕神鬼捉蛟龙。人所不常为之事。东人。如闾巷贱人。阳为知文字之状。而羞涩不能信口发言者。
明人假饰。可谓之文而不可谓之言。东人非文亦非言。其势固宜如此。明人之视为文。如捕神鬼捉蛟龙。人所不常为之事。东人。如闾巷贱人。阳为知文字之状。而羞涩不能信口发言者。东人之文。大率伤于四书注疏。其自以守正者。多支离缓弱。其尚奇者。以支离缓弱之资地。而稍取明人糟粕。以假饰其字句而已。惟简易。尚奇而不假饰。溪谷。守正而不缓弱。宜其并跱词坛哉。然二公各有遗恨。须合二公为一。然后可以望风欧,曾之门矣。
尤斋之文。盛矣。简易,溪谷之后一人矣。然有可论。且其欲学史迁处。不如其纯出于朱子者。
息庵尝曰。乐全胜玄轩。春沼胜乐全。是谓己又胜春沼也。乐全,春沼之文。余未之见焉。惟息庵。岂能胜玄轩。大抵皆有得于明人者。而玄轩较冲澹。此则又就其中。有古今之变。
朱子叹世俗为文。都是假底。而举其闻于人者曰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此减字法也。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也。东人为文。亦有用此法者。然减字法不至甚。惟换字法殊可恶。且无论地名。即于寻常行语间。分明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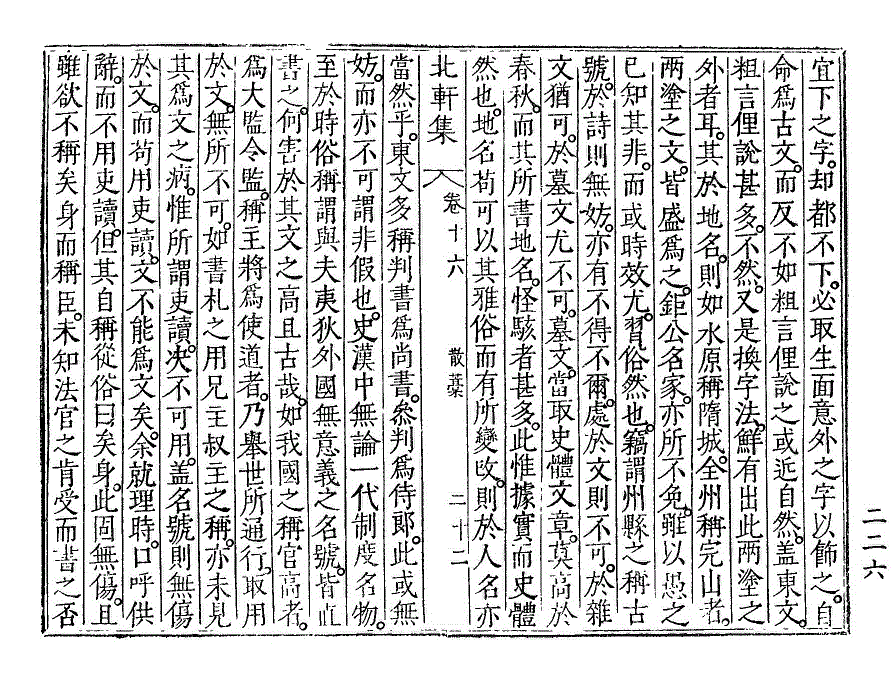 宜下之字。却都不下。必取生面意外之字以饰之。自命为古文。而反不如粗言俚说之或近自然。盖东文。粗言俚说甚多。不然。又是换字法。鲜有出此两涂之外者耳。其于地名。则如水原称隋城。全州称完山者。两涂之文。皆盛为之。钜公名家。亦所不免。虽以愚之已知其非。而或时效尤。习俗然也。窃谓州县之称古号。于诗则无妨。亦有不得不尔。处于文则不可。于杂文犹可。于墓文尤不可。墓文。当取史体文章。莫高于春秋。而其所书地名。怪骇者甚多。此惟据实而史体然也。地名苟可以其雅俗而有所变改。则于人名亦当然乎。东文多称判书为尚书。参判为侍郎。此或无妨。而亦不可谓非假也。史汉中无论一代制度名物。至于时俗称谓与夫夷狄外国无意义之名号。皆直书之。何害于其文之高且古哉。如我国之称官高者。为大监令监。称主将为使道者。乃举世所通行。取用于文。无所不可。如书札之用兄主叔主之称。亦未见其为文之病。惟所谓吏读。决不可用。盖名号则无伤于文。而苟用吏读。文不能为文矣。余就理时。口呼供辞。而不用吏读。但其自称从俗曰矣身。此固无伤。且虽欲不称矣身而称臣。未知法官之肯受而书之否
宜下之字。却都不下。必取生面意外之字以饰之。自命为古文。而反不如粗言俚说之或近自然。盖东文。粗言俚说甚多。不然。又是换字法。鲜有出此两涂之外者耳。其于地名。则如水原称隋城。全州称完山者。两涂之文。皆盛为之。钜公名家。亦所不免。虽以愚之已知其非。而或时效尤。习俗然也。窃谓州县之称古号。于诗则无妨。亦有不得不尔。处于文则不可。于杂文犹可。于墓文尤不可。墓文。当取史体文章。莫高于春秋。而其所书地名。怪骇者甚多。此惟据实而史体然也。地名苟可以其雅俗而有所变改。则于人名亦当然乎。东文多称判书为尚书。参判为侍郎。此或无妨。而亦不可谓非假也。史汉中无论一代制度名物。至于时俗称谓与夫夷狄外国无意义之名号。皆直书之。何害于其文之高且古哉。如我国之称官高者。为大监令监。称主将为使道者。乃举世所通行。取用于文。无所不可。如书札之用兄主叔主之称。亦未见其为文之病。惟所谓吏读。决不可用。盖名号则无伤于文。而苟用吏读。文不能为文矣。余就理时。口呼供辞。而不用吏读。但其自称从俗曰矣身。此固无伤。且虽欲不称矣身而称臣。未知法官之肯受而书之否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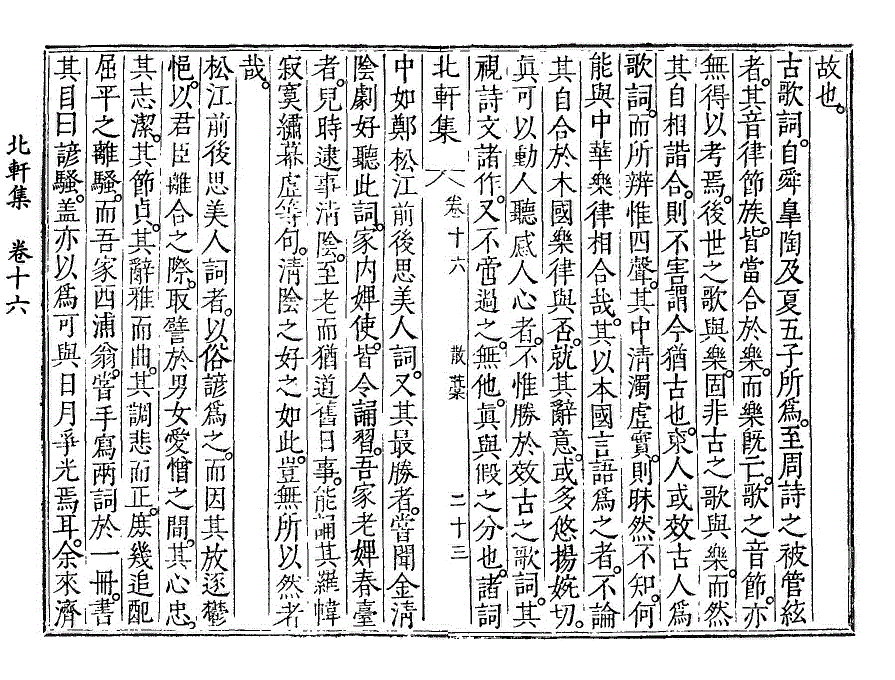 故也。
故也。古歌词。自舜皋陶及夏五子所为。至周诗之被管弦者。其音律节族。皆当合于乐。而乐既亡。歌之音节。亦无得以考焉。后世之歌与乐。固非古之歌与乐。而然其自相谐合。则不害谓今犹古也。东人或效古人为歌词。而所辨惟四声。其中清浊虚实。则昧然不知。何能与中华乐律相合哉。其以本国言语为之者。不论其自合于本国乐律与否。就其辞意。或多悠扬婉切。真可以动人听感人心者。不惟胜于效古之歌词。其视诗文诸作。又不啻过之。无他。真与假之分也。诸词中如郑松江前后思美人词。又其最胜者。尝闻金清阴剧好听此词。家内婢使。皆令诵习。吾家老婢春台者。儿时逮事清阴。至老而犹道旧日事。能诵其罗帏寂寞绣幕虚等句。清阴之好之如此。岂无所以然者哉。
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其放逐郁悒。以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悲而正。庶几追配屈平之离骚。而吾家西浦翁。尝手写两词于一册。书其目曰谚骚。盖亦以为可与日月争光焉耳。余来济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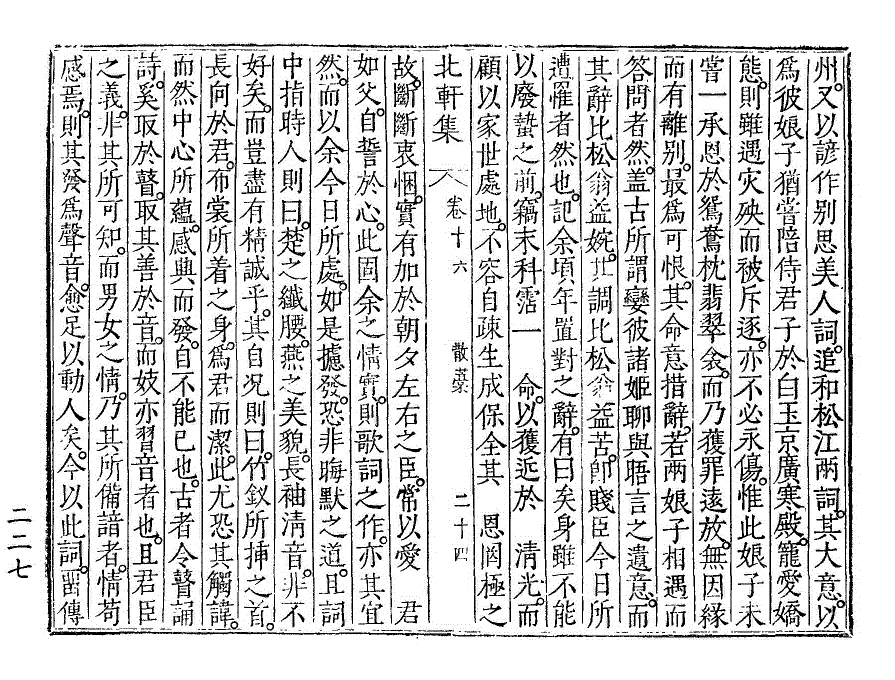 州。又以谚作别思美人词。追和松江两词。其大意。以为彼娘子犹尝陪侍君子于白玉京广寒殿。宠爱娇态。则虽遇灾殃而被斥逐。亦不必永伤。惟此娘子未尝一承恩于鸳鸯枕翡翠衾。而乃获罪远放。无因缘而有离别。最为可恨。其命意措辞。若两娘子相遇而答问者然。盖古所谓娈彼诸姬聊与晤言之遗意。而其辞比松翁益婉。其调比松翁益苦。即贱臣今日所遭罹者然也。记余顷年置对之辞。有曰矣身虽不能以废蛰之前。窃末科沾一 命。以获近于 清光。而顾以家世处地。不容自疏生成保全其 恩罔极之故。断断衷悃。实有加于朝夕左右之臣。常以爱 君如父。自誓于心。此固余之情实。则歌词之作。亦其宜然。而以余今日所处。如是摅发。恐非晦默之道。且词中指时人则曰。楚之纤腰。燕之美貌。长袖清音。非不好矣。而岂尽有精诚乎。其自况则曰。竹钗所插之首。长向于君。布裳所着之身。为君而洁。此尤恐其触讳。而然中心所蕴。感兴而发。自不能已也。古者令瞽诵诗。奚取于瞽。取其善于音。而妓亦习音者也。且君臣之义。非其所可知。而男女之情。乃其所备谙者。情苟感焉。则其发为声音。愈足以动人矣。今以此词。留传
州。又以谚作别思美人词。追和松江两词。其大意。以为彼娘子犹尝陪侍君子于白玉京广寒殿。宠爱娇态。则虽遇灾殃而被斥逐。亦不必永伤。惟此娘子未尝一承恩于鸳鸯枕翡翠衾。而乃获罪远放。无因缘而有离别。最为可恨。其命意措辞。若两娘子相遇而答问者然。盖古所谓娈彼诸姬聊与晤言之遗意。而其辞比松翁益婉。其调比松翁益苦。即贱臣今日所遭罹者然也。记余顷年置对之辞。有曰矣身虽不能以废蛰之前。窃末科沾一 命。以获近于 清光。而顾以家世处地。不容自疏生成保全其 恩罔极之故。断断衷悃。实有加于朝夕左右之臣。常以爱 君如父。自誓于心。此固余之情实。则歌词之作。亦其宜然。而以余今日所处。如是摅发。恐非晦默之道。且词中指时人则曰。楚之纤腰。燕之美貌。长袖清音。非不好矣。而岂尽有精诚乎。其自况则曰。竹钗所插之首。长向于君。布裳所着之身。为君而洁。此尤恐其触讳。而然中心所蕴。感兴而发。自不能已也。古者令瞽诵诗。奚取于瞽。取其善于音。而妓亦习音者也。且君臣之义。非其所可知。而男女之情。乃其所备谙者。情苟感焉。则其发为声音。愈足以动人矣。今以此词。留传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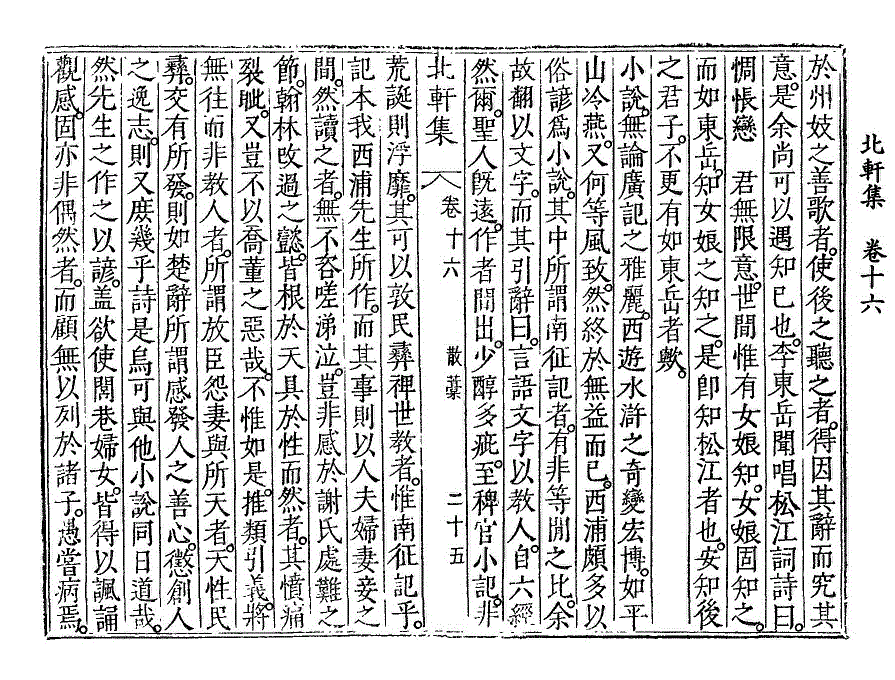 于州妓之善歌者。使后之听之者。得因其辞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己也。李东岳闻唱松江词诗曰。惆怅恋 君无限意。世间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东岳。知女娘之知之。是即知松江者也。安知后之君子。不更有如东岳者欤。
于州妓之善歌者。使后之听之者。得因其辞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己也。李东岳闻唱松江词诗曰。惆怅恋 君无限意。世间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东岳。知女娘之知之。是即知松江者也。安知后之君子。不更有如东岳者欤。小说。无论广记之雅丽。西游水浒之奇变宏博。如平山冷燕。又何等风致。然终于无益而已。西浦颇多以俗谚为小说。其中所谓南征记者。有非等閒之比。余故翻以文字。而其引辞曰。言语文字以教人。自六经然尔。圣人既远。作者间出。少醇多疵。至稗官小记。非荒诞则浮靡。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惟南征记乎。记本我西浦先生所作。而其事则以人夫妇妻妾之间。然读之者。无不咨嗟涕泣。岂非感于谢氏处难之节。翰林改过之懿。皆根于天具于性而然者。其愤痛裂眦。又岂不以乔董之恶哉。不惟如是。推类引义。将无往而非教人者。所谓放臣怨妻与所天者。天性民彝。交有所发。则如楚辞所谓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则又庶几乎诗是乌可与他小说同日道哉。然先生之作之以谚。盖欲使闾巷妇女。皆得以讽诵观感。固亦非偶然者。而顾无以列于诸子。愚尝病焉。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六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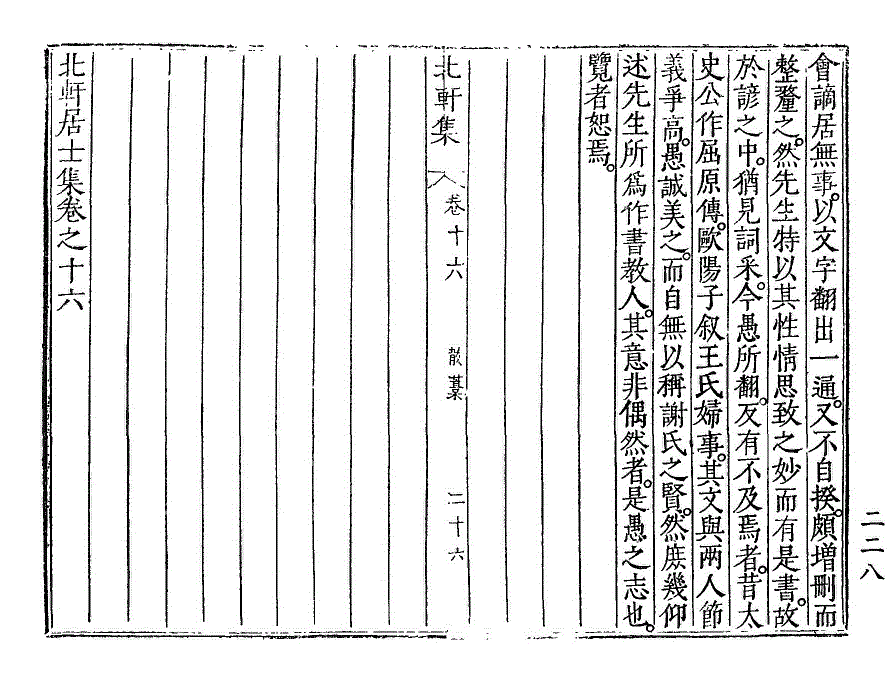 会谪居无事。以文字翻出一通。又不自揆。颇增删而整釐之。然先生特以其性情思致之妙而有是书。故于谚之中。犹见词采。今愚所翻。反有不及焉者。昔太史公作屈原传。欧阳子叙王氏妇事。其文与两人节义争高。愚诚美之。而自无以称谢氏之贤。然庶几仰述先生所为作书教人。其意非偶然者。是愚之志也。览者恕焉。
会谪居无事。以文字翻出一通。又不自揆。颇增删而整釐之。然先生特以其性情思致之妙而有是书。故于谚之中。犹见词采。今愚所翻。反有不及焉者。昔太史公作屈原传。欧阳子叙王氏妇事。其文与两人节义争高。愚诚美之。而自无以称谢氏之贤。然庶几仰述先生所为作书教人。其意非偶然者。是愚之志也。览者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