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囚海录(文)○书
囚海录(文)○书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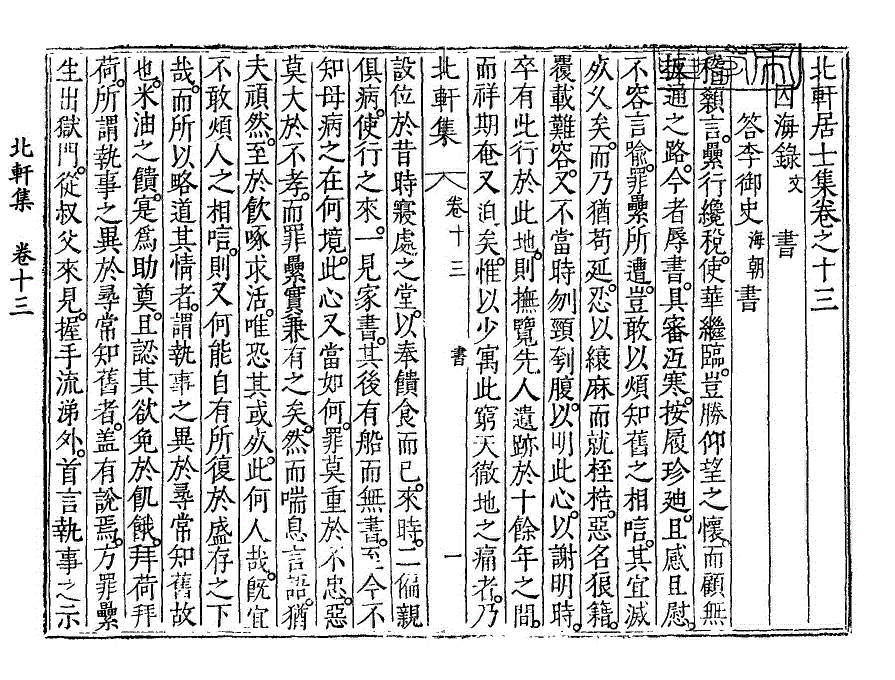 答李御史(海朝)书
答李御史(海朝)书稽颡言。累行才税。使华继临。岂胜仰望之怀。而顾无扳通之路。今者辱书。具审冱寒。按履珍迪。且感且慰。不容言喻。罪累所遭。岂敢以烦知旧之相唁。其宜灭死久矣。而乃犹苟延。忍以缞麻而就桎梏。恶名狼籍(一作藉)。覆载难容。又不当时刎颈刳腹。以明此心。以谢明时。卒有此行于此地。则抚览先人遗迹于十馀年之间。而祥期奄又迫矣。惟以少寓此穷天彻地之痛者。乃设位于昔时寝处之堂。以奉馈食而已。来时。二偏亲俱病。使行之来。一见家书。其后有船而无书。至今不知母病之在何境。此心又当如何。罪莫重于不忠。恶莫大于不孝。而罪累实兼有之矣。然而喘息言语。犹夫顽然。至于饮啄求活。唯恐其或死。此何人哉。既宜不敢烦人之相唁。则又何能自有所复于盛存之下哉。而所以略道其情者。谓执事之异于寻常知旧故也。米油之馈。寔为助奠。且认其欲免于饥饿。拜荷拜荷。所谓执事之异于寻常知旧者。盖有说焉。方罪累生出狱门。从叔父来见。握手流涕外。首言执事之示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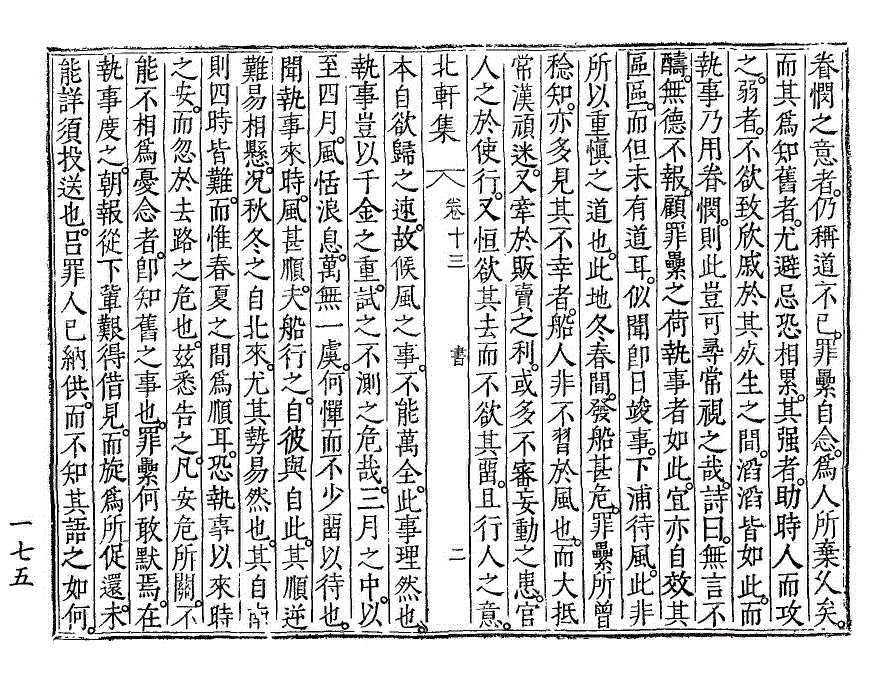 眷悯之意者。仍称道不已。罪累自念。为人所弃久矣。而其为知旧者。尤避忌恐相累。其强者。助时人而攻之。弱者。不欲致欣戚于其死生之间。滔滔皆如此。而执事乃用眷悯。则此岂可寻常视之哉。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顾罪累之荷执事者如此。宜亦自效其区区。而但未有道耳。似闻即日竣事。下浦待风。此非所以重慎之道也。此地冬春间。发船甚危。罪累所曾稔知。亦多见其不幸者。船人非不习于风也。而大抵常汉顽迷。又牵于贩卖之利。或多不审妄动之患。官人之于使行。又恒欲其去而不欲其留。且行人之意。本自欲归之速。故候风之事。不能万全。此事理然也。执事岂以千金之重。试之不测之危哉。三月之中。以至四月。风恬浪息。万无一虞。何惮而不少留以待也。闻执事来时。风甚顺。夫船行之。自彼与自此。其顺逆难易相悬。况秋冬之自北来。尤其势易然也。其自南则四时皆难。而惟春夏之间为顺耳。恐执事以来时之安。而忽于去路之危也。玆悉告之。凡安危所关。不能不相为忧念者。即知旧之事也。罪累何敢默焉。在执事度之。朝报从下辈艰得借见。而旋为所促还。未能详须投送也。吕罪人已纳供。而不知其语之如何。
眷悯之意者。仍称道不已。罪累自念。为人所弃久矣。而其为知旧者。尤避忌恐相累。其强者。助时人而攻之。弱者。不欲致欣戚于其死生之间。滔滔皆如此。而执事乃用眷悯。则此岂可寻常视之哉。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顾罪累之荷执事者如此。宜亦自效其区区。而但未有道耳。似闻即日竣事。下浦待风。此非所以重慎之道也。此地冬春间。发船甚危。罪累所曾稔知。亦多见其不幸者。船人非不习于风也。而大抵常汉顽迷。又牵于贩卖之利。或多不审妄动之患。官人之于使行。又恒欲其去而不欲其留。且行人之意。本自欲归之速。故候风之事。不能万全。此事理然也。执事岂以千金之重。试之不测之危哉。三月之中。以至四月。风恬浪息。万无一虞。何惮而不少留以待也。闻执事来时。风甚顺。夫船行之。自彼与自此。其顺逆难易相悬。况秋冬之自北来。尤其势易然也。其自南则四时皆难。而惟春夏之间为顺耳。恐执事以来时之安。而忽于去路之危也。玆悉告之。凡安危所关。不能不相为忧念者。即知旧之事也。罪累何敢默焉。在执事度之。朝报从下辈艰得借见。而旋为所促还。未能详须投送也。吕罪人已纳供。而不知其语之如何。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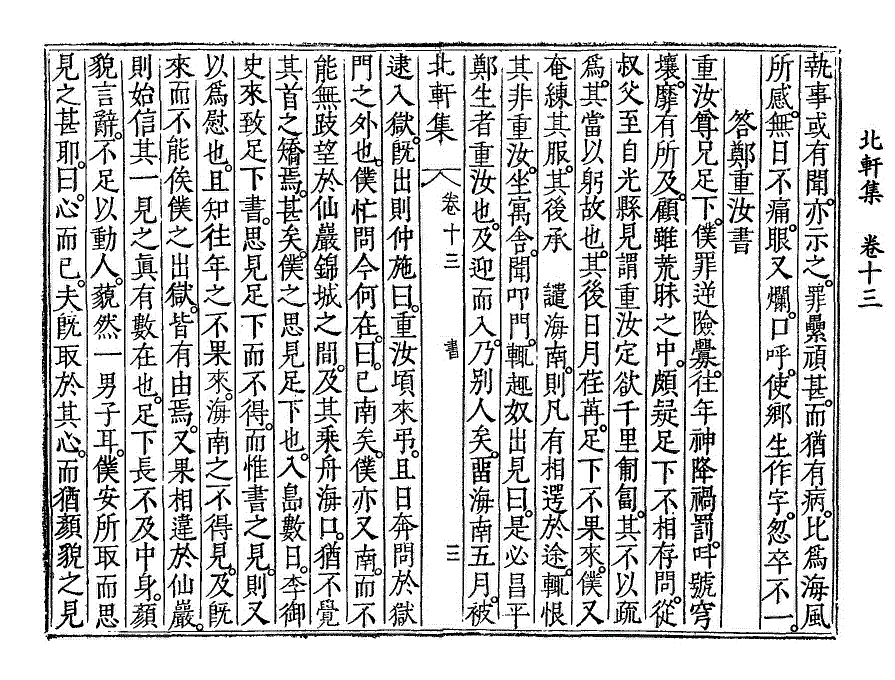 执事或有闻。亦示之。罪累顽甚。而犹有病。比为海风所感。无日不痛。眼又烂。口呼。使乡生作字。匆卒不一。
执事或有闻。亦示之。罪累顽甚。而犹有病。比为海风所感。无日不痛。眼又烂。口呼。使乡生作字。匆卒不一。答郑重汝书
重汝尊兄足下。仆罪逆险衅。往年神降祸罚。叫号穹壤。靡有所及。顾虽荒昧之中。颇疑足下不相存问。从叔父至自光县见谓重汝定欲千里匍匐。其不以疏为。其当以躬故也。其后日月荏苒。足下不果来。仆又奄练其服。其后承 谴海南。则凡有相遌于途。辄恨其非重汝。坐寓舍。闻叩门。辄趣奴出见曰。是必昌平郑生者重汝也。及迎而入。乃别人矣。留海南五月。被逮入狱。既出则仲施曰。重汝顷来吊。且日奔问于狱门之外也。仆忙问今何在。曰。已南矣。仆亦又南。而不能无跂望于仙岩锦城之间。及其乘舟海口。犹不觉其首之矫焉。甚矣。仆之思见足下也。入岛数日。李御史来致足下书。思见足下而不得。而惟书之见。则又以为慰也。且知往年之不果来。海南之不得见。及既来而不能俟仆之出狱。皆有由焉。又果相违于仙岩。则始信其一见之真有数在也。足下长不及中身。颜貌言辞。不足以动人。藐然一男子耳。仆安所取而思见之甚耶。曰。心而已。夫既取于其心。而犹颜貌之见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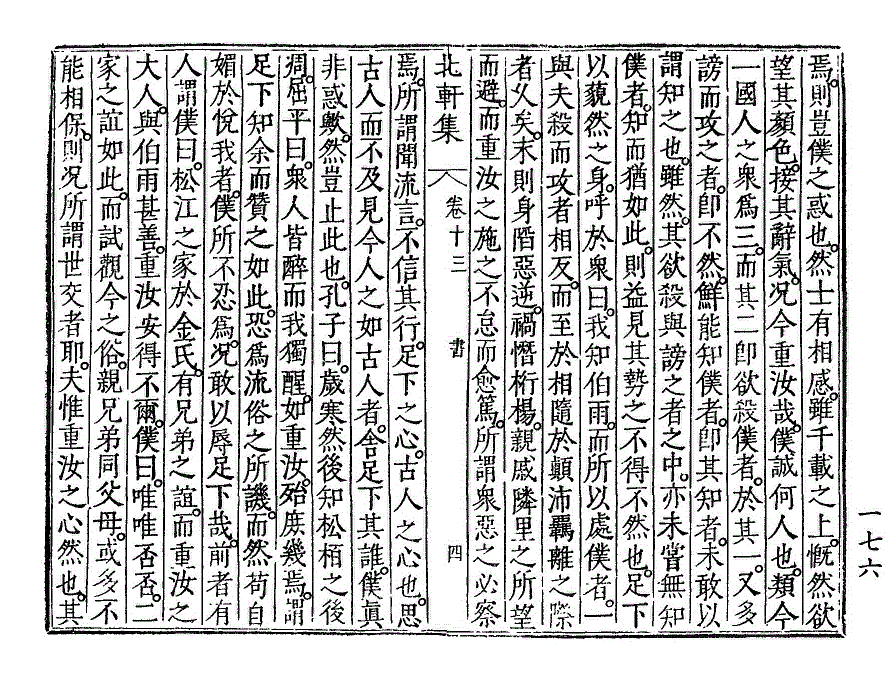 焉。则岂仆之惑也。然士有相感。虽千载之上。慨然欲望其颜色。接其辞气。况今重汝哉。仆诚何人也。类今一国人之众为三。而其二即欲杀仆者。于其一。又多谤而攻之者。即不然。鲜能知仆者。即其知者。未敢以谓知之也。虽然。其欲杀与谤之者之中。亦未尝无知仆者。知而犹如此。则益见其势之不得不然也。足下以藐然之身。呼于众曰。我知伯雨。而所以处仆者。一与夫杀而攻者相反。而至于相随于颠沛羁离之际者久矣。末则身陷恶逆。祸憯桁杨。亲戚邻里之所望而避。而重汝之施之不怠而愈笃。所谓众恶之必察焉。所谓闻流言。不信其行。足下之心。古人之心也。思古人而不及见今人之如古人者。舍足下其谁。仆真非惑欤。然岂止此也。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屈平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如重汝。殆庶几焉。谓足下知余而赞之如此。恐为流俗之所讥。而然苟自媚于悦我者。仆所不忍为。况敢以辱足下哉。前者有人谓仆曰。松江之家于金氏。有兄弟之谊。而重汝之大人。与伯雨甚善。重汝安得不尔。仆曰。唯唯否否。二家之谊如此。而试观今之俗。亲兄弟同父母。或多不能相保。则况所谓世交者耶。夫惟重汝之心然也。其
焉。则岂仆之惑也。然士有相感。虽千载之上。慨然欲望其颜色。接其辞气。况今重汝哉。仆诚何人也。类今一国人之众为三。而其二即欲杀仆者。于其一。又多谤而攻之者。即不然。鲜能知仆者。即其知者。未敢以谓知之也。虽然。其欲杀与谤之者之中。亦未尝无知仆者。知而犹如此。则益见其势之不得不然也。足下以藐然之身。呼于众曰。我知伯雨。而所以处仆者。一与夫杀而攻者相反。而至于相随于颠沛羁离之际者久矣。末则身陷恶逆。祸憯桁杨。亲戚邻里之所望而避。而重汝之施之不怠而愈笃。所谓众恶之必察焉。所谓闻流言。不信其行。足下之心。古人之心也。思古人而不及见今人之如古人者。舍足下其谁。仆真非惑欤。然岂止此也。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屈平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如重汝。殆庶几焉。谓足下知余而赞之如此。恐为流俗之所讥。而然苟自媚于悦我者。仆所不忍为。况敢以辱足下哉。前者有人谓仆曰。松江之家于金氏。有兄弟之谊。而重汝之大人。与伯雨甚善。重汝安得不尔。仆曰。唯唯否否。二家之谊如此。而试观今之俗。亲兄弟同父母。或多不能相保。则况所谓世交者耶。夫惟重汝之心然也。其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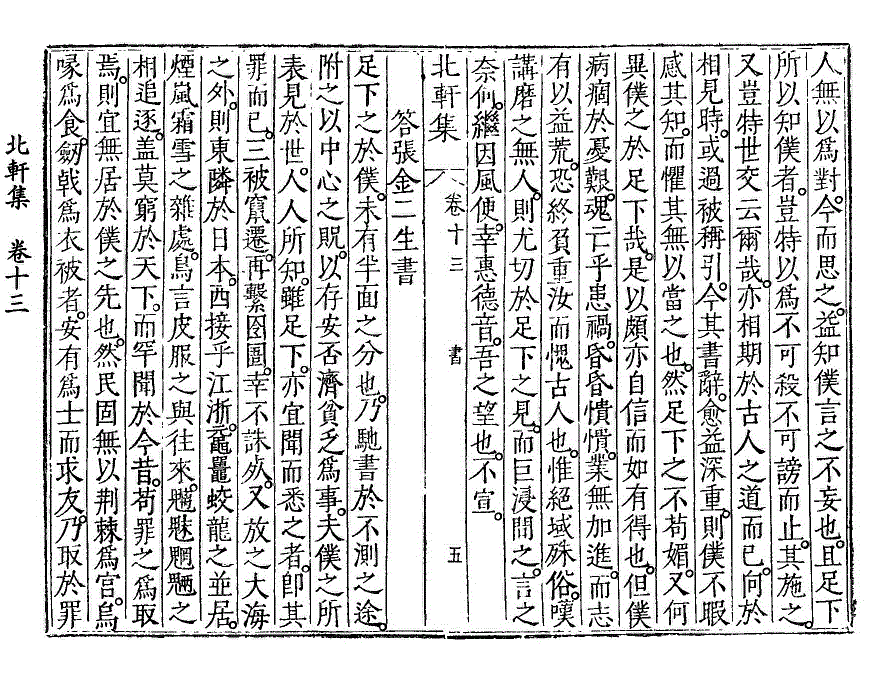 人无以为对。今而思之。益知仆言之不妄也。且足下所以知仆者。岂特以为不可杀不可谤而止。其施之。又岂特世交云尔哉。亦相期于古人之道而已。向于相见时。或过被称引。今其书辞。愈益深重。则仆不暇感其知。而惧其无以当之也。然足下之不苟媚。又何异仆之于足下哉。是以颇亦自信而如有得也。但仆病痼于忧艰。魂亡乎患祸。昏昏愦愦。业无加进。而志有以益荒。恐终负重汝而愧古人也。惟绝域殊俗。叹讲磨之无人。则尤切于足下之见。而巨浸间之。言之奈何。继因风便。幸惠德音。吾之望也。不宣。
人无以为对。今而思之。益知仆言之不妄也。且足下所以知仆者。岂特以为不可杀不可谤而止。其施之。又岂特世交云尔哉。亦相期于古人之道而已。向于相见时。或过被称引。今其书辞。愈益深重。则仆不暇感其知。而惧其无以当之也。然足下之不苟媚。又何异仆之于足下哉。是以颇亦自信而如有得也。但仆病痼于忧艰。魂亡乎患祸。昏昏愦愦。业无加进。而志有以益荒。恐终负重汝而愧古人也。惟绝域殊俗。叹讲磨之无人。则尤切于足下之见。而巨浸间之。言之奈何。继因风便。幸惠德音。吾之望也。不宣。答张金二生书
足下之于仆。未有半面之分也。乃驰书于不测之途。附之以中心之贶。以存安否济贫乏为事。夫仆之所表见于世。人人所知。虽足下。亦宜闻而悉之者。即其罪而已。三被窜迁。再系囹圄。幸不诛死。又放之大海之外。则东邻于日本。西接乎江浙。鼋鼍蛟龙之并居。烟岚霜雪之杂处。鸟言皮服之与往来。魑魅魍魉之相追逐。盖莫穷于天下。而罕闻于今昔。苟罪之为取焉。则宜无居于仆之先也。然民固无以荆棘为宫。乌喙为食。剑戟为衣被者。安有为士而求友。乃取于罪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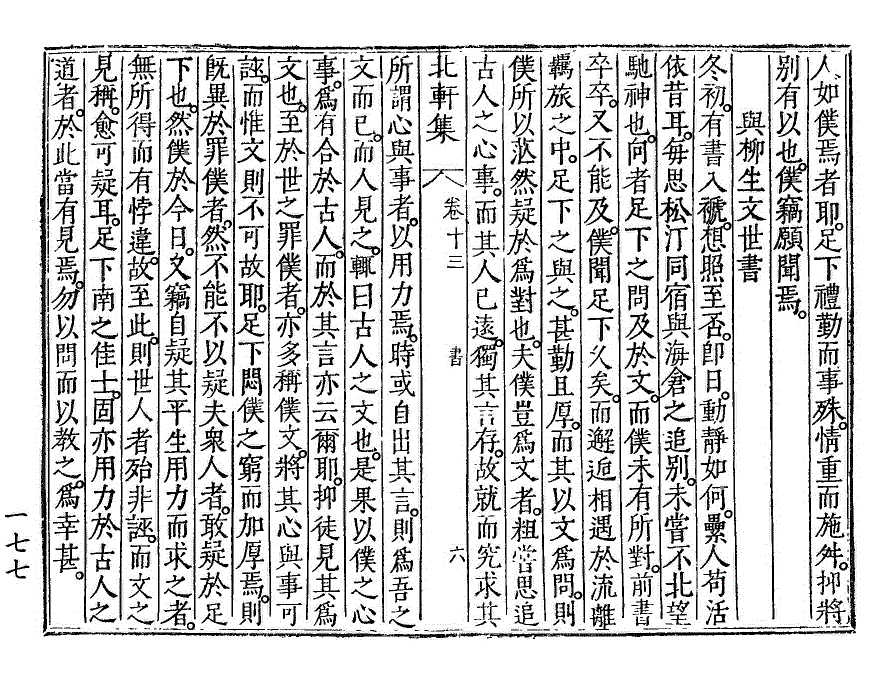 人如仆焉者耶。足下礼勤而事殊。情重而施舛。抑将别有以也。仆窃愿闻焉。
人如仆焉者耶。足下礼勤而事殊。情重而施舛。抑将别有以也。仆窃愿闻焉。与柳生文世书
冬初。有书入褫。想照至否。即日。动静如何。累人苟活依昔耳。每思松汀同宿与海仓之追别。未尝不北望驰神也。向者足下之问及于文。而仆未有所对。前书卒卒。又不能及。仆闻足下久矣。而邂逅相遇于流离羁旅之中。足下之与之。甚勤且厚。而其以文为问。则仆所以茫然疑于为对也。夫仆岂为文者。粗尝思追古人之心事。而其人已远。独其言存。故就而究求其所谓心与事者。以用力焉。时或自出其言。则为吾之文而已。而人见之。辄曰古人之文也。是果以仆之心事。为有合于古人。而于其言亦云尔耶。抑徒见其为文也。至于世之罪仆者。亦多称仆文。将其心与事可诬。而惟文则不可故耶。足下闷仆之穷而加厚焉。则既异于罪仆者。然不能不以疑夫众人者。敢疑于足下也。然仆于今日。又窃自疑其平生用力而求之者。无所得而有悖违。故至此。则世人者殆非诬。而文之见称。愈可疑耳。足下南之佳士。固亦用力于古人之道者。于此当有见焉。勿以问而以教之。为幸甚。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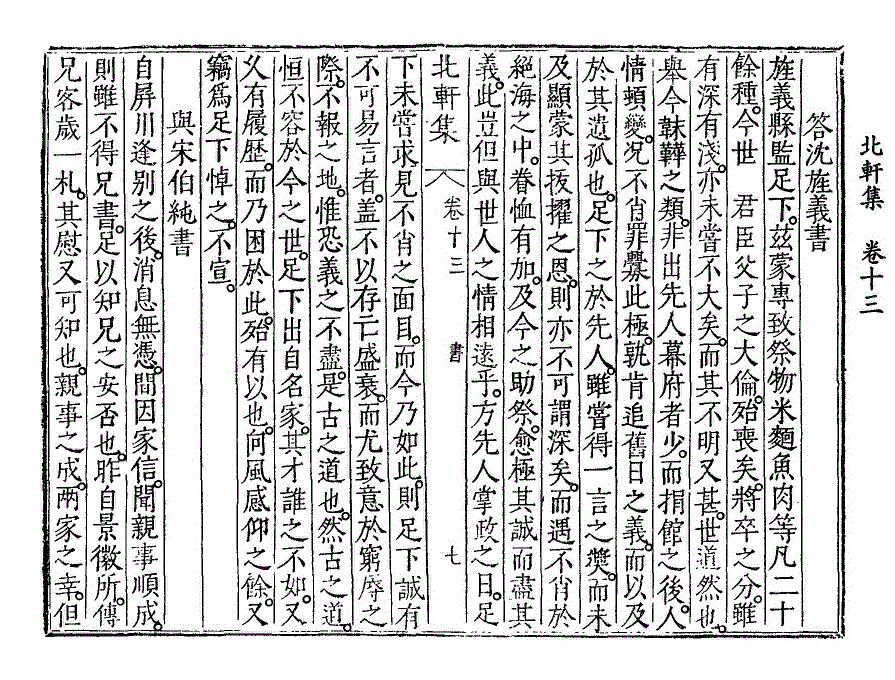 答沈旌义书
答沈旌义书旌义县监足下。玆蒙专致祭物米面鱼肉等凡二十馀种。今世 君臣父子之大伦。殆丧矣。将卒之分。虽有深有浅。亦未尝不大矣。而其不明又甚。世道然也。举今韎靴之类。非出先人幕府者少。而捐馆之后。人情顿变。况不肖罪衅此极。孰肯追旧日之义。而以及于其遗孤也。足下之于先人。虽尝得一言之奖。而未及显蒙其拔擢之恩。则亦不可谓深矣。而遇不肖于绝海之中。眷恤有加。及今之助祭。愈极其诚而尽其义。此岂但与世人之情相远乎。方先人掌政之日。足下未尝求见不肖之面目。而今乃如此。则足下诚有不可易言者。盖不以存亡盛衰。而尤致意于穷辱之际。不报之地。惟恐义之不尽。是古之道也。然古之道。恒不容于今之世。足下出自名家。其才谁之不如。又久有履历。而乃困于此。殆有以也。向风感仰之馀。又窃为足下悼之。不宣。
与宋伯纯书
自屏川逢别之后。消息无凭。间因家信。闻亲事顺成。则虽不得兄书。足以知兄之安否也。昨自景徽所。传兄客岁一札。其慰又可知也。亲事之成。两家之幸。但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8L 页
 兄于近日。苦不利于口。而犹无亲近罪人一条目。今乃添成谤案。想海涌山出。有不胜抵当。是弟奉贻者然也。然兄既不以置念。弟又何敢多言。惟女息实有不堪为法家妇者。人家儿少。无论男女。其有豪华气习者。最害于德。弟家之无此习。兄所知也。况弟一生流离穷困。为弟之子。而岂有豪华之理。惟其流离之故。此儿养于其外家。外家固亦寒素。而不幸前后携往于其任所。雄藩大都。使之饱食嬉游。遂以成习。其母之随弟于西迁南窜。井臼箕帚辛艰劳苦之事。此儿皆不见也。且以其不在弟侧之故。实无所教。即教之。弟又何能化之也。以其习豪且无教。而今乃猥为法家妇。岂其所堪耶。兄须痛加诲责。俾无大过则幸甚。弟之今日所处。不欲复言。但兄之于弟。颇尝有误知者存。故以弟为犹或可以堪遣于今日。此又误也。诚以悲忧感愤之积。精神几尽散亡。外虽起居言语。其中则无异病狂之人。尝验之看书。才过数叶。辄茫然惛然殆不能辨其口读。即旧所熟讲之书。亦然。往时岂其如此。此皆摧伤沉没。不可以复为人者。虽欲自奋。末由也已。古人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弟虽不敢自期。如吾兄者。未
兄于近日。苦不利于口。而犹无亲近罪人一条目。今乃添成谤案。想海涌山出。有不胜抵当。是弟奉贻者然也。然兄既不以置念。弟又何敢多言。惟女息实有不堪为法家妇者。人家儿少。无论男女。其有豪华气习者。最害于德。弟家之无此习。兄所知也。况弟一生流离穷困。为弟之子。而岂有豪华之理。惟其流离之故。此儿养于其外家。外家固亦寒素。而不幸前后携往于其任所。雄藩大都。使之饱食嬉游。遂以成习。其母之随弟于西迁南窜。井臼箕帚辛艰劳苦之事。此儿皆不见也。且以其不在弟侧之故。实无所教。即教之。弟又何能化之也。以其习豪且无教。而今乃猥为法家妇。岂其所堪耶。兄须痛加诲责。俾无大过则幸甚。弟之今日所处。不欲复言。但兄之于弟。颇尝有误知者存。故以弟为犹或可以堪遣于今日。此又误也。诚以悲忧感愤之积。精神几尽散亡。外虽起居言语。其中则无异病狂之人。尝验之看书。才过数叶。辄茫然惛然殆不能辨其口读。即旧所熟讲之书。亦然。往时岂其如此。此皆摧伤沉没。不可以复为人者。虽欲自奋。末由也已。古人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弟虽不敢自期。如吾兄者。未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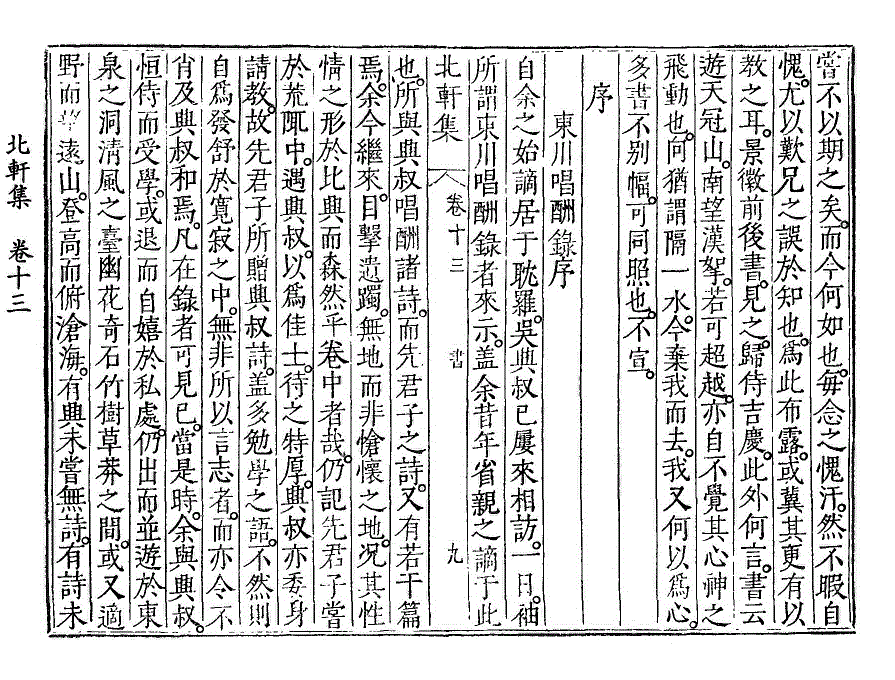 尝不以期之矣。而今何如也。每念之愧汗。然不暇自愧。尤以叹兄之误于知也。为此布露。或冀其更有以教之耳。景徽前后书。见之。归侍吉庆。此外何言。书云游天冠山。南望汉挐。若可超越。亦自不觉其心神之飞动也。向犹谓隔一水。今弃我而去。我又何以为心。多书不别幅。可同照也。不宣。
尝不以期之矣。而今何如也。每念之愧汗。然不暇自愧。尤以叹兄之误于知也。为此布露。或冀其更有以教之耳。景徽前后书。见之。归侍吉庆。此外何言。书云游天冠山。南望汉挐。若可超越。亦自不觉其心神之飞动也。向犹谓隔一水。今弃我而去。我又何以为心。多书不别幅。可同照也。不宣。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囚海录(文)○序
东川唱酬录序
自余之始谪居于耽罗。吴兴叔已屡来相访。一日。袖所谓东川唱酬录者来示。盖余昔年省亲之谪于此也。所与兴叔唱酬诸诗。而先君子之诗。又有若干篇焉。余今继来。目击遗躅。无地而非怆怀之地。况其性情之形于比兴而森然乎卷中者哉。仍记先君子尝于荒陬中。遇兴叔。以为佳士。待之特厚。兴叔亦委身请教。故先君子所赠兴叔诗。盖多勉学之语。不然则自为发舒于宽寂之中。无非所以言志者。而亦令不肖及兴叔和焉。凡在录者可见已。当是时。余与兴叔。恒侍而受学。或退而自嬉于私处。仍出而并游于东泉之洞清风之台幽花奇石竹树草莽之间。或又适野而望远山。登高而俯沧海。有兴未尝无诗。有诗未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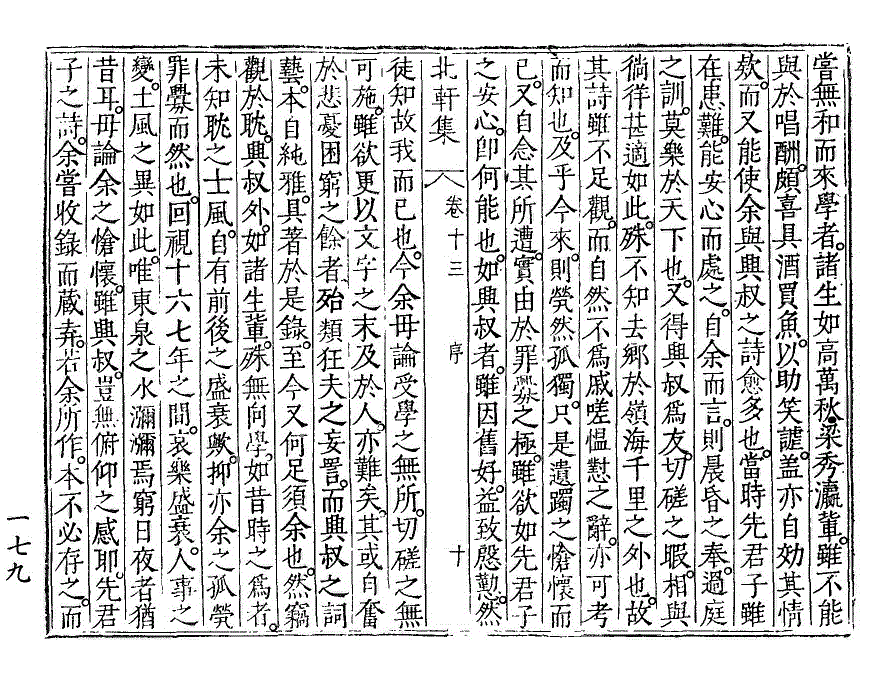 尝无和而来学者。诸生如高万秋,梁秀瀛辈。虽不能与于唱酬。颇喜具酒买鱼。以助笑谑。盖亦自效其情款。而又能使余与兴叔之诗愈多也。当时先君子虽在患难。能安心而处之。自余而言。则晨昏之奉。过庭之训。莫乐于天下也。又得兴叔为友。切磋之暇。相与徜徉甚适如此。殊不知去乡于岭海千里之外也。故其诗虽不足观。而自然不为戚嗟愠怼之辞。亦可考而知也。及乎今来。则茕然孤独。只是遗躅之怆怀而已。又自念其所遭。实由于罪衅之极。虽欲如先君子之安心。即何能也。如兴叔者。虽因旧好。益致慇勤。然徒知故我而已也。今余毋论受学之无所。切磋之无可施。虽欲更以文字之末及于人。亦难矣。其或自奋于悲忧困穷之馀者。殆类狂夫之妄詈。而兴叔之词艺。本自纯雅。具著于是录。至今又何足须余也。然窃观于耽。兴叔外。如诸生辈。殊无向学。如昔时之为者。未知耽之士风。自有前后之盛衰欤。抑亦余之孤茕罪衅而然也。回视十六七年之间。哀乐盛衰。人事之变。土风之异如此。唯东泉之水㳽㳽焉穷日夜者犹昔耳。毋论余之怆怀。虽兴叔。岂无俯仰之感耶。先君子之诗。余尝收录而藏弆。若余所作。本不必存之。而
尝无和而来学者。诸生如高万秋,梁秀瀛辈。虽不能与于唱酬。颇喜具酒买鱼。以助笑谑。盖亦自效其情款。而又能使余与兴叔之诗愈多也。当时先君子虽在患难。能安心而处之。自余而言。则晨昏之奉。过庭之训。莫乐于天下也。又得兴叔为友。切磋之暇。相与徜徉甚适如此。殊不知去乡于岭海千里之外也。故其诗虽不足观。而自然不为戚嗟愠怼之辞。亦可考而知也。及乎今来。则茕然孤独。只是遗躅之怆怀而已。又自念其所遭。实由于罪衅之极。虽欲如先君子之安心。即何能也。如兴叔者。虽因旧好。益致慇勤。然徒知故我而已也。今余毋论受学之无所。切磋之无可施。虽欲更以文字之末及于人。亦难矣。其或自奋于悲忧困穷之馀者。殆类狂夫之妄詈。而兴叔之词艺。本自纯雅。具著于是录。至今又何足须余也。然窃观于耽。兴叔外。如诸生辈。殊无向学。如昔时之为者。未知耽之士风。自有前后之盛衰欤。抑亦余之孤茕罪衅而然也。回视十六七年之间。哀乐盛衰。人事之变。土风之异如此。唯东泉之水㳽㳽焉穷日夜者犹昔耳。毋论余之怆怀。虽兴叔。岂无俯仰之感耶。先君子之诗。余尝收录而藏弆。若余所作。本不必存之。而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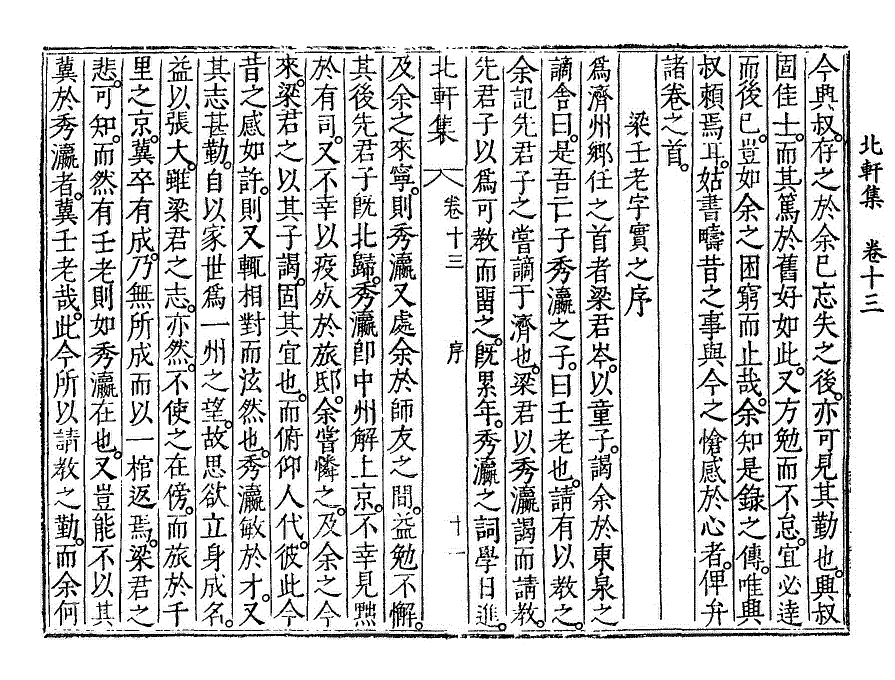 今兴叔。存之于余已忘失之后。亦可见其勤也。兴叔固佳士。而其笃于旧好如此。又方勉而不怠。宜必达而后已。岂如余之困穷而止哉。余知是录之传。唯兴叔赖焉耳。姑书畴昔之事与今之怆感于心者。俾弁诸卷之首。
今兴叔。存之于余已忘失之后。亦可见其勤也。兴叔固佳士。而其笃于旧好如此。又方勉而不怠。宜必达而后已。岂如余之困穷而止哉。余知是录之传。唯兴叔赖焉耳。姑书畴昔之事与今之怆感于心者。俾弁诸卷之首。梁壬老字实之序
为济州乡任之首者梁君岑。以童子。谒余于东泉之谪舍曰。是吾亡子秀瀛之子。曰壬老也。请有以教之。余记先君子之尝谪于济也。梁君以秀瀛谒而请教。先君子以为可教而留之。既累年。秀瀛之词学日进。及余之来宁。则秀瀛又处余于师友之间。益勉不懈。其后先君子既北归。秀瀛即中州解上京。不幸见黜于有司。又不幸以疫死于旅邸。余尝怜之。及余之今来。梁君之以其子谒。固其宜也。而俯仰人代。彼此今昔之感如许。则又辄相对而泫然也。秀瀛敏于才。又其志甚勤。自以家世为一州之望。故思欲立身成名。益以张大。虽梁君之志。亦然。不使之在傍。而旅于千里之京。冀卒有成。乃无所成而以一棺返焉。梁君之悲。可知。而然有壬老则如秀瀛在也。又岂能不以其冀于秀瀛者。冀壬老哉。此今所以请教之勤。而余何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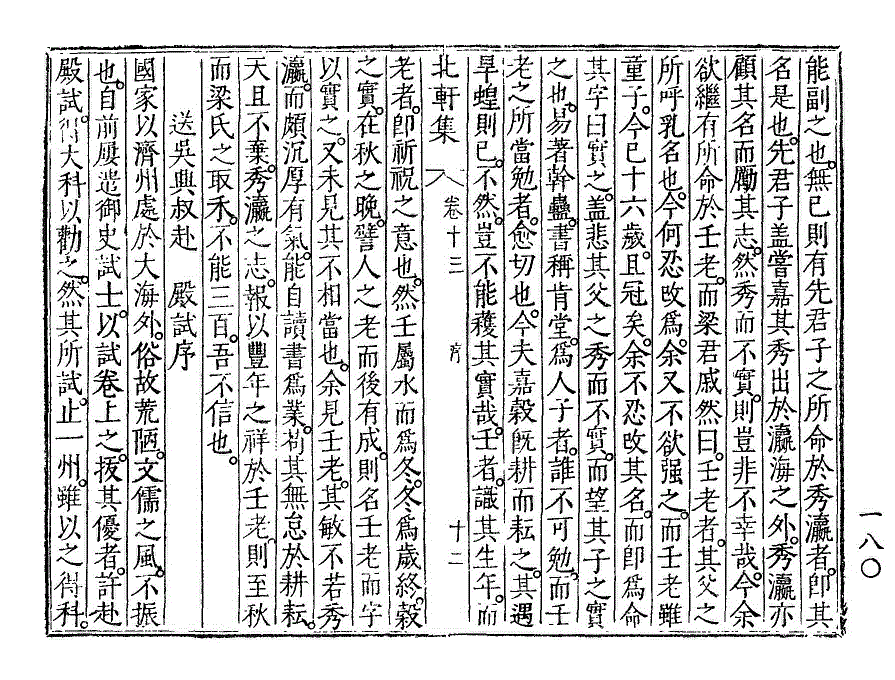 能副之也。无己则有先君子之所命于秀瀛者。即其名是也。先君子盖尝嘉其秀出于瀛海之外。秀瀛亦顾其名而励其志。然秀而不实。则岂非不幸哉。今余欲继有所命于壬老。而梁君戚然曰。壬老者。其父之所呼乳名也。今何忍改为。余又不欲强之。而壬老虽童子。今已十六岁。且冠矣。余不忍改其名。而即为命其字曰实之。盖悲其父之秀而不实。而望其子之实之也。易著干蛊。书称肯堂。为人子者。谁不可勉。而壬老之所当勉者。愈切也。今夫嘉谷既耕而耘之。其遇旱蝗则已。不然。岂不能穫其实哉。壬者。识其生年。而老者。即祈祝之意也。然壬属水而为冬。冬为岁终。谷之实。在秋之晚。譬人之老而后有成。则名壬老而字以实之。又未见其不相当也。余见壬老。其敏不若秀瀛。而颇沉厚有气。能自读书为业。苟其无怠于耕耘。天且不弃。秀瀛之志。报以丰年之祥于壬老。则至秋而梁氏之取禾。不能三百。吾不信也。
能副之也。无己则有先君子之所命于秀瀛者。即其名是也。先君子盖尝嘉其秀出于瀛海之外。秀瀛亦顾其名而励其志。然秀而不实。则岂非不幸哉。今余欲继有所命于壬老。而梁君戚然曰。壬老者。其父之所呼乳名也。今何忍改为。余又不欲强之。而壬老虽童子。今已十六岁。且冠矣。余不忍改其名。而即为命其字曰实之。盖悲其父之秀而不实。而望其子之实之也。易著干蛊。书称肯堂。为人子者。谁不可勉。而壬老之所当勉者。愈切也。今夫嘉谷既耕而耘之。其遇旱蝗则已。不然。岂不能穫其实哉。壬者。识其生年。而老者。即祈祝之意也。然壬属水而为冬。冬为岁终。谷之实。在秋之晚。譬人之老而后有成。则名壬老而字以实之。又未见其不相当也。余见壬老。其敏不若秀瀛。而颇沉厚有气。能自读书为业。苟其无怠于耕耘。天且不弃。秀瀛之志。报以丰年之祥于壬老。则至秋而梁氏之取禾。不能三百。吾不信也。送吴兴叔赴 殿试序
国家以济州处于大海外。俗故荒陋。文儒之风。不振也。自前屡遣御史试士。以试卷上之。拔其优者。许赴殿试。得大科以劝之。然其所试。止一州。虽以之得科。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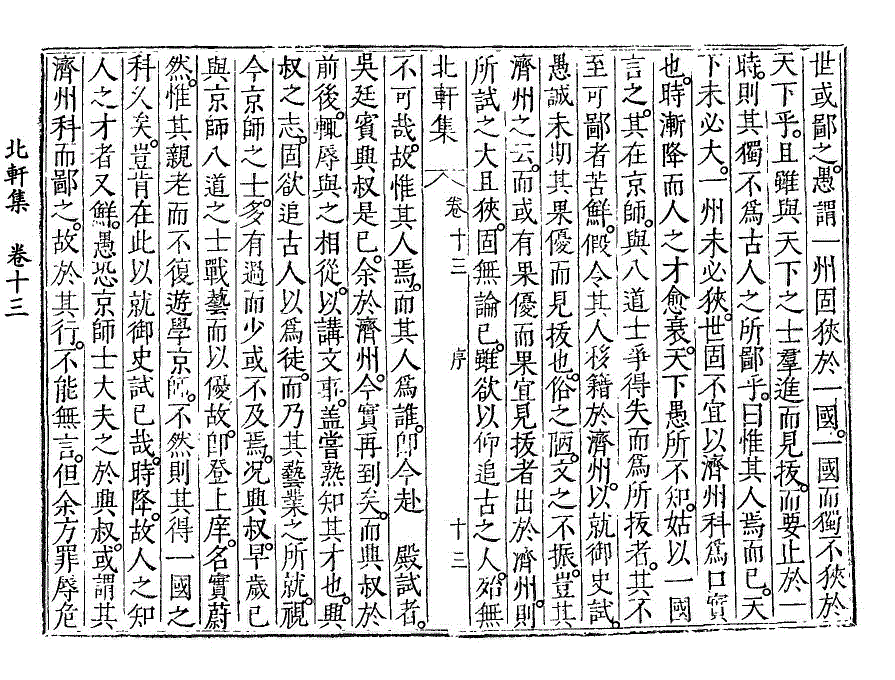 世或鄙之。愚谓一州固狭于一国。一国而独不狭于天下乎。且虽与天下之士群进而见拔。而要止于一时。则其独不为古人之所鄙乎。曰惟其人焉而已。天下未必大。一州未必狭。世固不宜以济州科为口实也。时渐降而人之才愈衰。天下愚所不知。姑以一国言之。其在京师。与八道士争得失而为所拔者。其不至可鄙者苦鲜。假令其人移籍于济州。以就御史试。愚诚未期其果优而见拔也。俗之陋。文之不振。岂其济州之云。而或有果优而果宜见拔者出于济州。则所试之大且狭。固无论已。虽欲以仰追古之人。殆无不可哉。故惟其人焉。而其人为谁。即今赴 殿试者。吴廷宾兴叔是已。余于济州。今实再到矣。而兴叔于前后。辄辱与之相从。以讲文事。盖尝熟知其才也。兴叔之志。固欲追古人以为徒。而乃其艺业之所就。视今京师之士。多有过而少或不及焉。况兴叔。早岁已与京师八道之士战艺而以优故。即登上庠。名实蔚然。惟其亲老而不复游学京师。不然则其得一国之科久矣。岂肯在此以就御史试已哉。时降。故人之知人之才者又鲜。愚恐京师士大夫之于兴叔。或谓其济州科而鄙之。故于其行。不能无言。但余方罪辱危
世或鄙之。愚谓一州固狭于一国。一国而独不狭于天下乎。且虽与天下之士群进而见拔。而要止于一时。则其独不为古人之所鄙乎。曰惟其人焉而已。天下未必大。一州未必狭。世固不宜以济州科为口实也。时渐降而人之才愈衰。天下愚所不知。姑以一国言之。其在京师。与八道士争得失而为所拔者。其不至可鄙者苦鲜。假令其人移籍于济州。以就御史试。愚诚未期其果优而见拔也。俗之陋。文之不振。岂其济州之云。而或有果优而果宜见拔者出于济州。则所试之大且狭。固无论已。虽欲以仰追古之人。殆无不可哉。故惟其人焉。而其人为谁。即今赴 殿试者。吴廷宾兴叔是已。余于济州。今实再到矣。而兴叔于前后。辄辱与之相从。以讲文事。盖尝熟知其才也。兴叔之志。固欲追古人以为徒。而乃其艺业之所就。视今京师之士。多有过而少或不及焉。况兴叔。早岁已与京师八道之士战艺而以优故。即登上庠。名实蔚然。惟其亲老而不复游学京师。不然则其得一国之科久矣。岂肯在此以就御史试已哉。时降。故人之知人之才者又鲜。愚恐京师士大夫之于兴叔。或谓其济州科而鄙之。故于其行。不能无言。但余方罪辱危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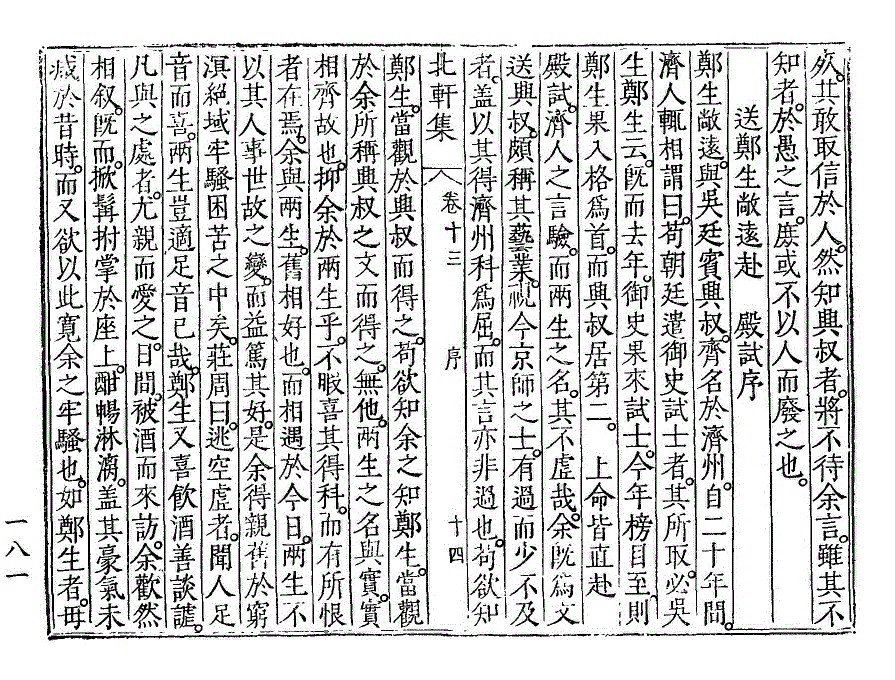 死。其敢取信于人。然知兴叔者。将不待余言。虽其不知者。于愚之言。庶或不以人而废之也。
死。其敢取信于人。然知兴叔者。将不待余言。虽其不知者。于愚之言。庶或不以人而废之也。送郑生敞远赴 殿试序
郑生敞远。与吴廷宾兴叔。齐名于济州。自二十年间。济人辄相谓曰。苟朝廷遣御史试士者。其所取。必吴生郑生云。既而去年。御史果来试士。今年榜目至。则郑生果入格为首。而兴叔居第二。 上命皆直赴 殿试。济人之言验。而两生之名。其不虚哉。余既为文送兴叔。颇称其艺业。视今京师之士。有过而少不及者。盖以其得济州科为屈。而其言亦非过也。苟欲知郑生。当观于兴叔而得之。苟欲知余之知郑生。当观于余所称兴叔之文而得之。无他。两生之名与实。实相齐故也。抑余于两生乎。不暇喜其得科。而有所恨者在焉。余与两生。旧相好也。而相遇于今日。两生不以其人事世故之变。而益笃其好。是余得亲旧于穷溟绝域牢骚困苦之中矣。庄周曰。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而喜。两生岂适足音已哉。郑生又喜饮酒善谈谑。凡与之处者。尤亲而爱之。日间。被酒而来访。余欢然相叙。既而。掀髯拊掌于座上。酣畅淋漓。盖其豪气未减于昔时。而又欲以此宽余之牢骚也。如郑生者。毋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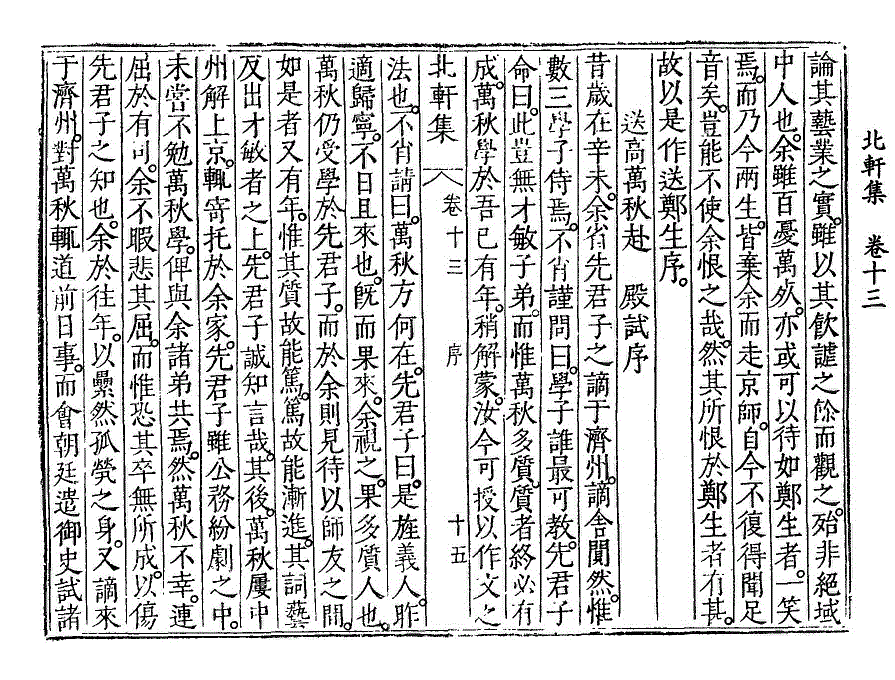 论其艺业之实。虽以其饮谑之馀而观之。殆非绝域中人也。余虽百忧万死。亦或可以待如郑生者。一笑焉。而乃今两生。皆弃余而走京师。自今不复得闻足音矣。岂能不使余恨之哉。然其所恨于郑生者有甚。故以是作送郑生序。
论其艺业之实。虽以其饮谑之馀而观之。殆非绝域中人也。余虽百忧万死。亦或可以待如郑生者。一笑焉。而乃今两生。皆弃余而走京师。自今不复得闻足音矣。岂能不使余恨之哉。然其所恨于郑生者有甚。故以是作送郑生序。送高万秋赴 殿试序
昔岁在辛未。余省先君子之谪于济州。谪舍阒然。惟数三学子侍焉。不肖谨问曰。学子谁最可教。先君子命曰。此岂无才敏子弟。而惟万秋多质。质者终必有成。万秋学于吾已有年。稍解蒙。汝今可授以作文之法也。不肖请曰。万秋方何在。先君子曰。是旌义人。昨适归宁。不日且来也。既而果来。余视之。果多质人也。万秋仍受学于先君子。而于余则见待以师友之间。如是者又有年。惟其质故能笃。笃故能渐进。其词艺反出才敏者之上。先君子诚知言哉。其后。万秋屡中州解上京。辄寄托于余家。先君子虽公务纷剧之中。未尝不勉万秋学。俾与余诸弟共焉。然万秋不幸。连屈于有司。余不暇悲其屈。而惟恐其卒无所成。以伤先君子之知也。余于往年。以累然孤茕之身。又谪来于济州。对万秋辄道前日事。而会朝廷遣御史试诸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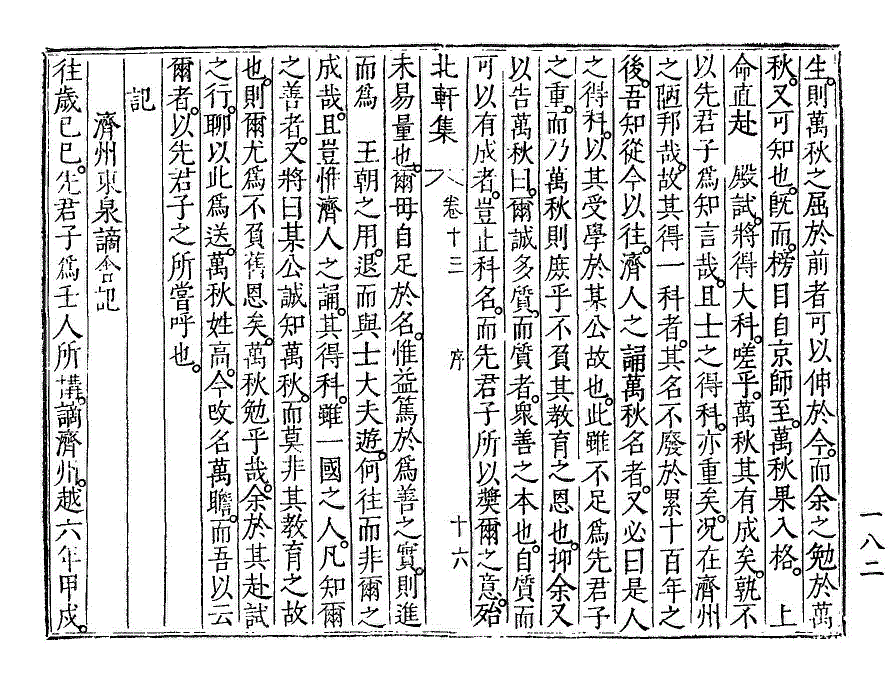 生。则万秋之屈于前者可以伸于今。而余之勉于万秋。又可知也。既而。榜目自京师至。万秋果入格。 上命直赴 殿试。将得大科。嗟乎。万秋其有成矣。孰不以先君子为知言哉。且士之得科。亦重矣。况在济州之陋邦哉。故其得一科者。其名不废于累十百年之后。吾知从今以往。济人之诵万秋名者。又必曰是人之得科。以其受学于某公故也。此虽不足为先君子之重。而乃万秋则庶乎不负其教育之恩也。抑余又以告万秋曰。尔诚多质。而质者。众善之本也。自质而可以有成者。岂止科名。而先君子所以奖尔之意。殆未易量也。尔毋自足于名。惟益笃于为善之实。则进而为 王朝之用。退而与士大夫游。何往而非尔之成哉。且岂惟济人之诵。其得科。虽一国之人。凡知尔之善者。又将曰某公诚知万秋。而莫非其教育之故也。则尔尤为不负旧恩矣。万秋勉乎哉。余于其赴试之行。聊以此为送。万秋姓高。今改名万瞻。而吾以云尔者。以先君子之所尝呼也。
生。则万秋之屈于前者可以伸于今。而余之勉于万秋。又可知也。既而。榜目自京师至。万秋果入格。 上命直赴 殿试。将得大科。嗟乎。万秋其有成矣。孰不以先君子为知言哉。且士之得科。亦重矣。况在济州之陋邦哉。故其得一科者。其名不废于累十百年之后。吾知从今以往。济人之诵万秋名者。又必曰是人之得科。以其受学于某公故也。此虽不足为先君子之重。而乃万秋则庶乎不负其教育之恩也。抑余又以告万秋曰。尔诚多质。而质者。众善之本也。自质而可以有成者。岂止科名。而先君子所以奖尔之意。殆未易量也。尔毋自足于名。惟益笃于为善之实。则进而为 王朝之用。退而与士大夫游。何往而非尔之成哉。且岂惟济人之诵。其得科。虽一国之人。凡知尔之善者。又将曰某公诚知万秋。而莫非其教育之故也。则尔尤为不负旧恩矣。万秋勉乎哉。余于其赴试之行。聊以此为送。万秋姓高。今改名万瞻。而吾以云尔者。以先君子之所尝呼也。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囚海录(文)○记
济州东泉谪舍记
往岁己巳。先君子为壬人所搆。谪济州。越六年甲戌。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3H 页
 当 更化还朝。越十一年甲申。捐馆舍。越三年丙戌。不肖春泽。又被前壬人之党之齮龁。未及释衰而谪于济。其距昔之来觐。实十有六年也。既下舟入城。则州使按法府关文。将安接余于民舍。问所欲居。余曰。其惟先君子之尝所居焉者乎。遂就而居之。济之为地。海道一千里。风波之虞不测。至则炎蒸雾雨。非人所堪。无论其氓俗陋薄。生理艰荒。即草木土石朝夕百物接乎人之耳目者。莫不绝异于陆。陆之声信。苟不得便风。或阻绝累月逾岁。虽官于此者。亦皆怖畏忧戚。若患难然。况谪乎哉。故凡罪名之极重者。幸不杀死。则必于此而困辱之。岂不以其地之最穷于国中也。夫人之于其先父兄之所留迹。虽其寻常经过之地。已又偶然而至焉。无不触目兴思而不能忘者。人之情也。而况前后谪于玆地乎哉。况余方忧疚之中而览昔日之迹者。其情又可知也。舍如旧。或有所增。凡为房者四。于是就先君子尝所寝处之房。设位以馈奠朝夕。就尝所置奴仆等者。为余兴居之所。馀又置今奴仆。则凡州人之旧相识者。既来吊余。又环顾踌躇。不觉其人事之已变。十年之为久。而即未尝相识者。亦皆感叹不已。况余之痛之哉。患难者。人所
当 更化还朝。越十一年甲申。捐馆舍。越三年丙戌。不肖春泽。又被前壬人之党之齮龁。未及释衰而谪于济。其距昔之来觐。实十有六年也。既下舟入城。则州使按法府关文。将安接余于民舍。问所欲居。余曰。其惟先君子之尝所居焉者乎。遂就而居之。济之为地。海道一千里。风波之虞不测。至则炎蒸雾雨。非人所堪。无论其氓俗陋薄。生理艰荒。即草木土石朝夕百物接乎人之耳目者。莫不绝异于陆。陆之声信。苟不得便风。或阻绝累月逾岁。虽官于此者。亦皆怖畏忧戚。若患难然。况谪乎哉。故凡罪名之极重者。幸不杀死。则必于此而困辱之。岂不以其地之最穷于国中也。夫人之于其先父兄之所留迹。虽其寻常经过之地。已又偶然而至焉。无不触目兴思而不能忘者。人之情也。而况前后谪于玆地乎哉。况余方忧疚之中而览昔日之迹者。其情又可知也。舍如旧。或有所增。凡为房者四。于是就先君子尝所寝处之房。设位以馈奠朝夕。就尝所置奴仆等者。为余兴居之所。馀又置今奴仆。则凡州人之旧相识者。既来吊余。又环顾踌躇。不觉其人事之已变。十年之为久。而即未尝相识者。亦皆感叹不已。况余之痛之哉。患难者。人所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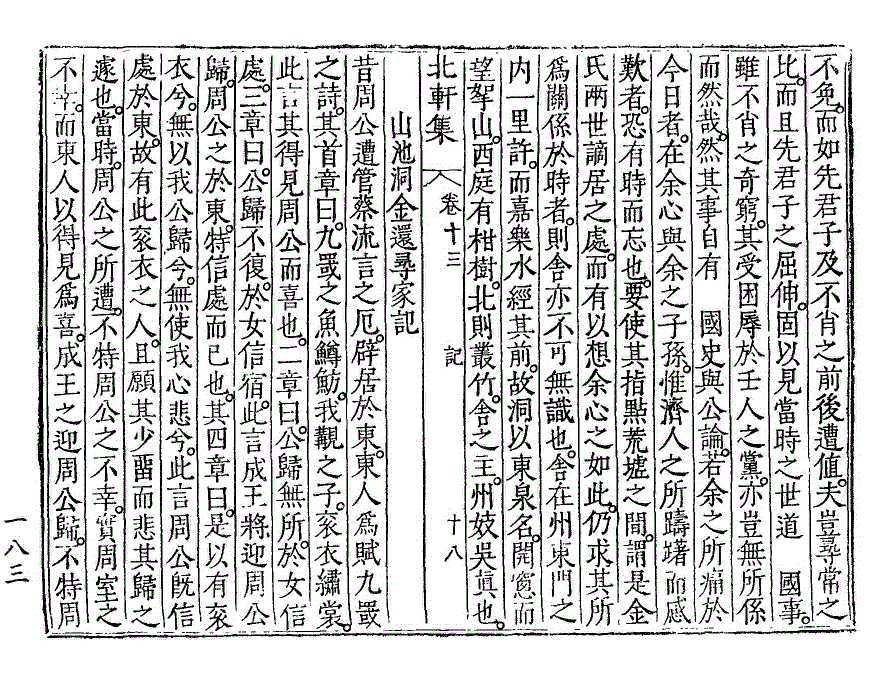 不免。而如先君子及不肖之前后遭值。夫岂寻常之比。而且先君子之屈伸。固以见当时之世道 国事。虽不肖之奇穷。其受困辱于壬人之党。亦岂无所系而然哉。然其事自有 国史与公论。若余之所痛于今日者。在余心与余之子孙。惟济人之所踌躇而感叹者。恐有时而忘也。要使其指点荒墟之间。谓是金氏两世谪居之处。而有以想余心之如此。仍求其所为关系于时者。则舍亦不可无识也。舍在州东门之内一里许。而嘉乐水经其前。故洞以东泉名。开窗而望挐山。西庭有柑树。北则丛竹。舍之主。州妓吴真也。
不免。而如先君子及不肖之前后遭值。夫岂寻常之比。而且先君子之屈伸。固以见当时之世道 国事。虽不肖之奇穷。其受困辱于壬人之党。亦岂无所系而然哉。然其事自有 国史与公论。若余之所痛于今日者。在余心与余之子孙。惟济人之所踌躇而感叹者。恐有时而忘也。要使其指点荒墟之间。谓是金氏两世谪居之处。而有以想余心之如此。仍求其所为关系于时者。则舍亦不可无识也。舍在州东门之内一里许。而嘉乐水经其前。故洞以东泉名。开窗而望挐山。西庭有柑树。北则丛竹。舍之主。州妓吴真也。山池洞金还寻家记
昔周公遭管蔡流言之厄。辟居于东。东人为赋九罭之诗。其首章曰。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此言其得见周公而喜也。二章曰。公归无所。于女信处。三章曰。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此言成王将迎周公归。周公之于东。特信处而已也。其四章曰。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此言周公既信处于东。故有此衮衣之人。且愿其少留而悲其归之遽也。当时。周公之所遭。不特周公之不幸。实周室之不幸。而东人以得见为喜。成王之迎周公归。不特周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4H 页
 室之幸。实亦东人之幸。而东人乃愿其留而悲其归也。假令成王不悟流言。周公不为所迎。而又不得安于东。终以快管蔡欲杀之心。则东人之悲。尤何如哉。向在己巳岁。尤庵宋先生。以独传周公之道之故。不容于时。而放于耽罗。耽固海外莫穷之异域。苟非朝鲜与先生之不幸。则耽人岂有得见先生之理。此其为喜。当不啻东人之于周公矣。未几。先生随金吾郎而去耽。卒被祸于途。朝鲜之不遂亡。盖幸。而此乃天地之间莫大之变。实所谓周公之不得安于东。管蔡之快其欲杀之心者。虽天下万世之人。当涕泣裂眦。况论一国一时。又况论耽人之悲哉。然以其得见于不当得见。而其去也如此。则其悲又可知也。且先生之于周公。其道固无以异矣。而所遭之时不同。周公则惟管蔡而已。而又即斯得而致辟。先生则虽 明主追悟于六年之后。雪其冤伸其枉。而举世犹多管蔡之党也。耽以海外故。其人朴而野。不足以为管蔡之党。而仅足以知周公之为周公。又可见耽人之悲之诚也。虽然。耽人之于先生。不可谓不知。而亦不能深知焉。则以其陋故也。嗟乎。先生当天下尽陷为夷狄禽兽之日。独能传周公之道。使朝鲜不失其礼义
室之幸。实亦东人之幸。而东人乃愿其留而悲其归也。假令成王不悟流言。周公不为所迎。而又不得安于东。终以快管蔡欲杀之心。则东人之悲。尤何如哉。向在己巳岁。尤庵宋先生。以独传周公之道之故。不容于时。而放于耽罗。耽固海外莫穷之异域。苟非朝鲜与先生之不幸。则耽人岂有得见先生之理。此其为喜。当不啻东人之于周公矣。未几。先生随金吾郎而去耽。卒被祸于途。朝鲜之不遂亡。盖幸。而此乃天地之间莫大之变。实所谓周公之不得安于东。管蔡之快其欲杀之心者。虽天下万世之人。当涕泣裂眦。况论一国一时。又况论耽人之悲哉。然以其得见于不当得见。而其去也如此。则其悲又可知也。且先生之于周公。其道固无以异矣。而所遭之时不同。周公则惟管蔡而已。而又即斯得而致辟。先生则虽 明主追悟于六年之后。雪其冤伸其枉。而举世犹多管蔡之党也。耽以海外故。其人朴而野。不足以为管蔡之党。而仅足以知周公之为周公。又可见耽人之悲之诚也。虽然。耽人之于先生。不可谓不知。而亦不能深知焉。则以其陋故也。嗟乎。先生当天下尽陷为夷狄禽兽之日。独能传周公之道。使朝鲜不失其礼义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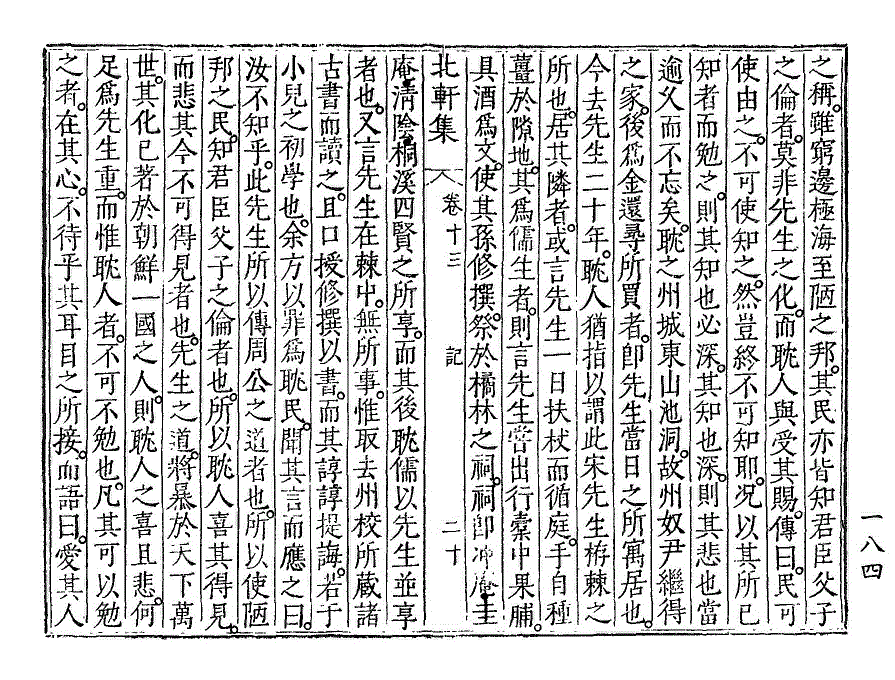 之称。虽穷边极海至陋之邦。其民亦皆知君臣父子之伦者。莫非先生之化。而耽人与受其赐。传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岂终不可知耶。况以其所已知者而勉之。则其知也必深。其知也深。则其悲也当逾久而不忘矣。耽之州城东山池洞。故州奴尹继得之家。后为金还寻所买者。即先生当日之所寓居也。今去先生二十年。耽人犹指以谓此宋先生栫棘之所也。居其邻者。或言先生一日扶杖而循庭。手自种姜于隙地。其为儒生者。则言先生尝出行橐中果脯。具酒为文。使其孙修撰。祭于橘林之祠。祠即冲庵,圭庵,清阴,桐溪四贤之所享。而其后耽儒以先生并享者也。又言先生在棘中。无所事。惟取去州校所藏诸古书而读之。且口授修撰以书。而其谆谆提诲。若于小儿之初学也。余方以罪为耽民。闻其言而应之曰。汝不知乎。此先生所以传周公之道者也。所以使陋邦之民。知君臣父子之伦者也。所以耽人喜其得见。而悲其今不可得见者也。先生之道。将暴于天下万世。其化已著于朝鲜一国之人。则耽人之喜且悲。何足为先生重。而惟耽人者。不可不勉也。凡其可以勉之者。在其心。不待乎其耳目之所接。而语曰。爱其人
之称。虽穷边极海至陋之邦。其民亦皆知君臣父子之伦者。莫非先生之化。而耽人与受其赐。传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岂终不可知耶。况以其所已知者而勉之。则其知也必深。其知也深。则其悲也当逾久而不忘矣。耽之州城东山池洞。故州奴尹继得之家。后为金还寻所买者。即先生当日之所寓居也。今去先生二十年。耽人犹指以谓此宋先生栫棘之所也。居其邻者。或言先生一日扶杖而循庭。手自种姜于隙地。其为儒生者。则言先生尝出行橐中果脯。具酒为文。使其孙修撰。祭于橘林之祠。祠即冲庵,圭庵,清阴,桐溪四贤之所享。而其后耽儒以先生并享者也。又言先生在棘中。无所事。惟取去州校所藏诸古书而读之。且口授修撰以书。而其谆谆提诲。若于小儿之初学也。余方以罪为耽民。闻其言而应之曰。汝不知乎。此先生所以传周公之道者也。所以使陋邦之民。知君臣父子之伦者也。所以耽人喜其得见。而悲其今不可得见者也。先生之道。将暴于天下万世。其化已著于朝鲜一国之人。则耽人之喜且悲。何足为先生重。而惟耽人者。不可不勉也。凡其可以勉之者。在其心。不待乎其耳目之所接。而语曰。爱其人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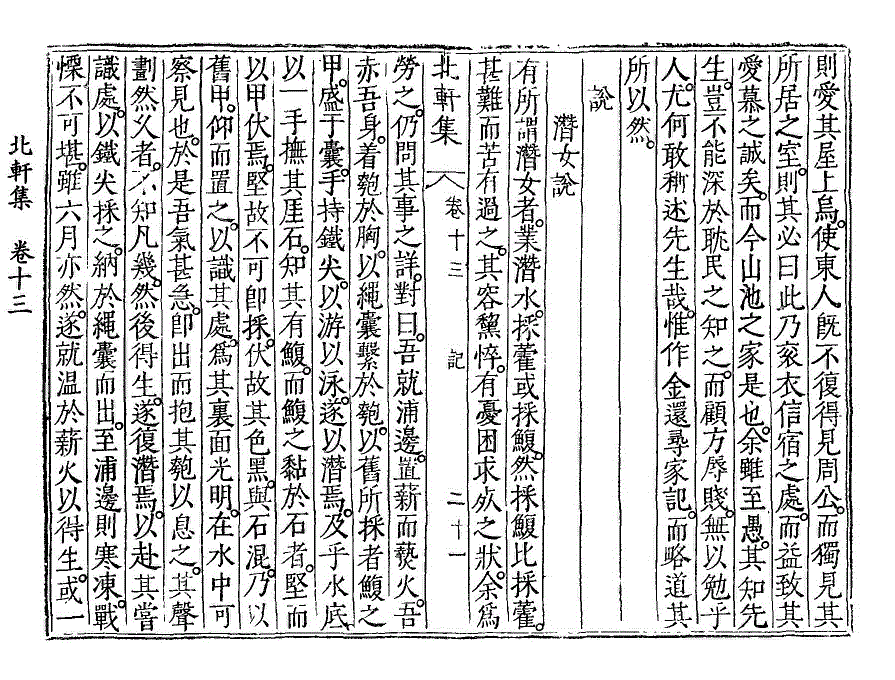 则爱其屋上乌。使东人既不复得见周公。而独见其所居之室。则其必曰此乃衮衣信宿之处。而益致其爱慕之诚矣。而今山池之家是也。余虽至愚。其知先生。岂不能深于耽民之知之。而顾方辱贱。无以勉乎人。尤何敢称述先生哉。惟作金还寻家记。而略道其所以然。
则爱其屋上乌。使东人既不复得见周公。而独见其所居之室。则其必曰此乃衮衣信宿之处。而益致其爱慕之诚矣。而今山池之家是也。余虽至愚。其知先生。岂不能深于耽民之知之。而顾方辱贱。无以勉乎人。尤何敢称述先生哉。惟作金还寻家记。而略道其所以然。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囚海录(文)○说
潜女说
有所谓潜女者。业潜水。采藿或采鳆。然采鳆比采藿。甚难而苦有过之。其容黧悴。有忧困求死之状。余为劳之。仍问其事之详。对曰。吾就浦边。置薪而爇火。吾赤吾身。着匏于胸。以绳囊系于匏。以旧所采者鳆之甲。盛于囊。手持铁尖。以游以泳。遂以潜焉。及乎水底。以一手抚其厓石。知其有鳆。而鳆之黏于石者。坚而以甲伏焉。坚故不可即采。伏故其色黑。与石混。乃以旧甲。仰而置之。以识其处。为其里面光明。在水中可察见也。于是吾气甚急。即出而抱其匏以息之。其声划然久者。不知凡几。然后得生。遂复潜焉。以赴其尝识处。以铁尖采之。纳于绳囊而出。至浦边则寒冻。战慄不可堪。虽六月亦然。遂就温于薪火以得生。或一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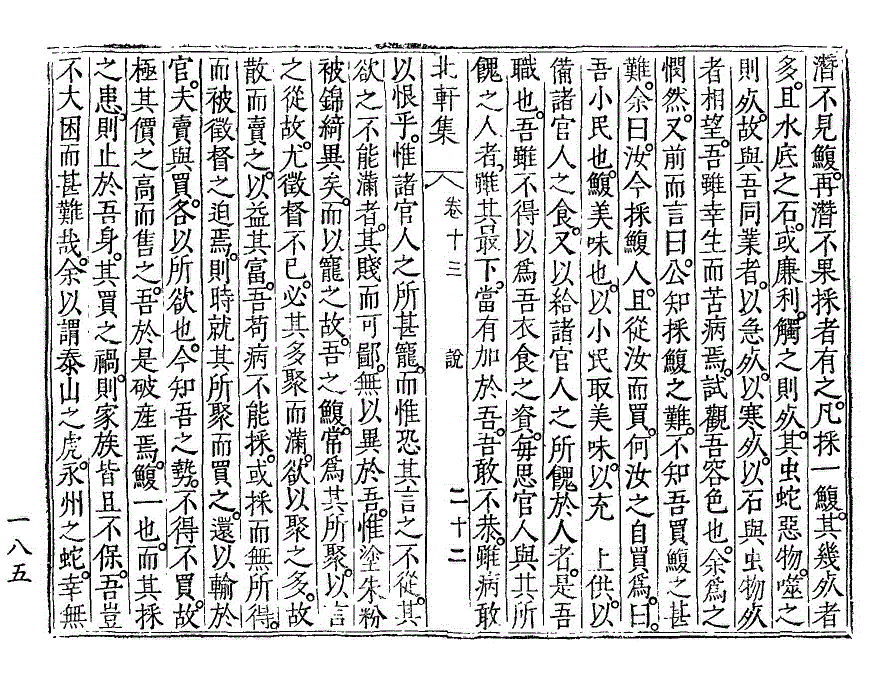 潜不见鳆。再潜不果采者有之。凡采一鳆。其几死者多。且水底之石。或廉利。触之则死。其虫蛇恶物。噬之则死。故与吾同业者。以急死。以寒死。以石与虫物死者相望。吾虽幸生而苦病焉。试观吾容色也。余为之悯然。又前而言曰。公知采鳆之难。不知吾买鳆之甚难。余曰。汝今采鳆人。且从汝而买。何汝之自买为。曰。吾小民也。鳆美味也。以小民取美味。以充 上供。以备诸官人之食。又以给诸官人之所馈于人者。是吾职也。吾虽不得以为吾衣食之资。每思官人与其所馈之人者。虽其最下。当有加于吾。吾敢不恭。虽病敢以恨乎。惟诸官人之所甚宠。而惟恐其言之不从。其欲之不能满者。其贱而可鄙。无以异于吾。惟涂朱粉被锦绮异矣。而以宠之故。吾之鳆。常为其所聚。以言之从故。尤徵督不已。必其多聚而满。欲以聚之多。故散而卖之。以益其富。吾苟病不能采。或采而无所得。而被徵督之迫焉。则时就其所聚而买之。还以输于官。夫卖与买。各以所欲也。今知吾之势。不得不买。故极其价之高而售之。吾于是破产焉。鳆一也。而其采之患。则止于吾身。其买之祸。则家族皆且不保。吾岂不大困而甚难哉。余以谓泰山之虎。永州之蛇。幸无
潜不见鳆。再潜不果采者有之。凡采一鳆。其几死者多。且水底之石。或廉利。触之则死。其虫蛇恶物。噬之则死。故与吾同业者。以急死。以寒死。以石与虫物死者相望。吾虽幸生而苦病焉。试观吾容色也。余为之悯然。又前而言曰。公知采鳆之难。不知吾买鳆之甚难。余曰。汝今采鳆人。且从汝而买。何汝之自买为。曰。吾小民也。鳆美味也。以小民取美味。以充 上供。以备诸官人之食。又以给诸官人之所馈于人者。是吾职也。吾虽不得以为吾衣食之资。每思官人与其所馈之人者。虽其最下。当有加于吾。吾敢不恭。虽病敢以恨乎。惟诸官人之所甚宠。而惟恐其言之不从。其欲之不能满者。其贱而可鄙。无以异于吾。惟涂朱粉被锦绮异矣。而以宠之故。吾之鳆。常为其所聚。以言之从故。尤徵督不已。必其多聚而满。欲以聚之多。故散而卖之。以益其富。吾苟病不能采。或采而无所得。而被徵督之迫焉。则时就其所聚而买之。还以输于官。夫卖与买。各以所欲也。今知吾之势。不得不买。故极其价之高而售之。吾于是破产焉。鳆一也。而其采之患。则止于吾身。其买之祸。则家族皆且不保。吾岂不大困而甚难哉。余以谓泰山之虎。永州之蛇。幸无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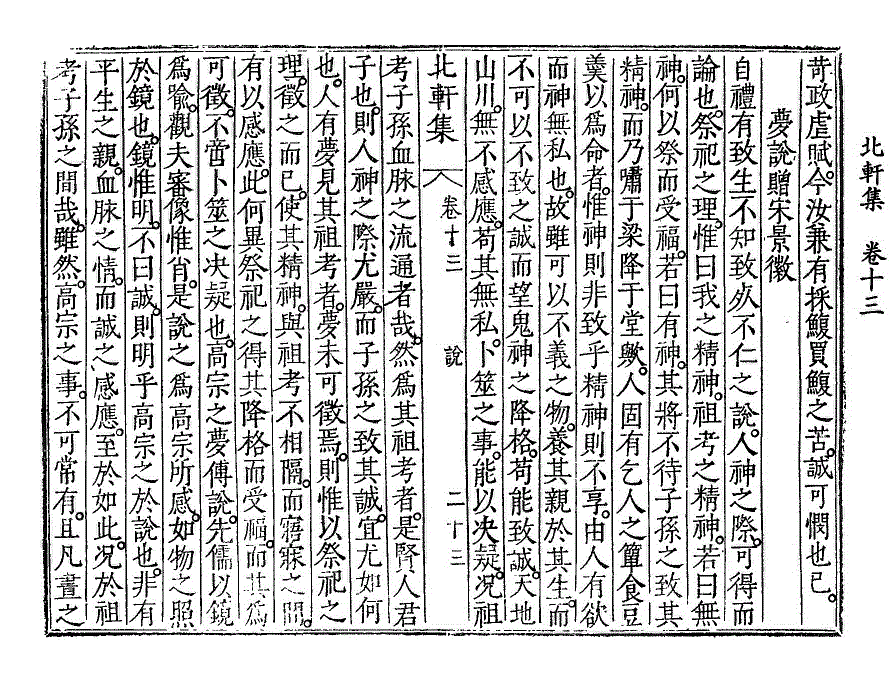 苛政虐赋。今汝兼有采鳆买鳆之苦。诚可悯也已。
苛政虐赋。今汝兼有采鳆买鳆之苦。诚可悯也已。梦说赠宋景徽
自礼有致生不知致死不仁之说。人神之际。可得而论也。祭祀之理。惟曰我之精神。祖考之精神。若曰无神。何以祭而受福。若曰有神。其将不待子孙之致其精神。而乃啸于梁降于堂欤。人固有乞人之箪食豆羹以为命者。惟神则非致乎精神则不享。由人有欲而神无私也。故虽可以不义之物。养其亲于其生。而不可以不致之诚而望鬼神之降格。苟能致诚。天地山川。无不感应。苟其无私。卜筮之事。能以决疑。况祖考子孙血脉之流通者哉。然为其祖考者。是贤人君子也。则人神之际尤严。而子孙之致其诚。宜尤如何也。人有梦见其祖考者。梦未可徵焉。则惟以祭祀之理。徵之而已。使其精神。与祖考不相隔。而寤寐之间。有以感应。此何异祭祀之得其降格而受福。而其为可徵。不啻卜筮之决疑也。高宗之梦傅说。先儒以镜为喻。观夫审像惟肖。是说之为高宗所感。如物之照于镜也。镜惟明。不曰诚。则明乎高宗之于说也。非有平生之亲。血脉之情。而诚之感应。至于如此。况于祖考子孙之间哉。虽然。高宗之事。不可常有。且凡昼之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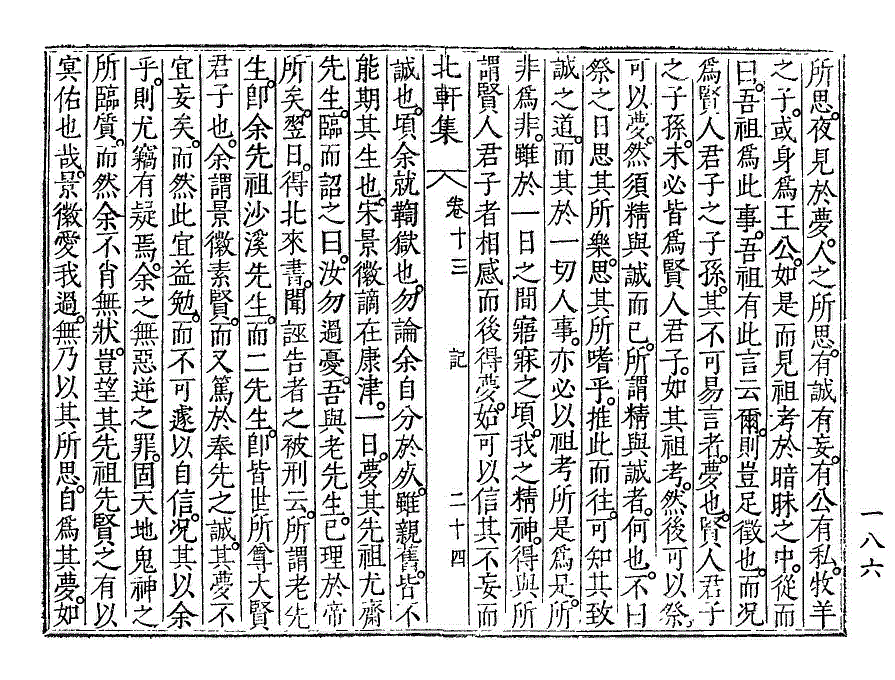 所思。夜见于梦。人之所思。有诚有妄。有公有私。牧羊之子。或身为王公。如是而见祖考于暗昧之中。从而曰。吾祖为此事。吾祖有此言云尔。则岂足徵也。而况为贤人君子之子孙。其不可易言者。梦也。贤人君子之子孙。未必皆为贤人君子。如其祖考。然后可以祭。可以梦。然须精与诚而已。所谓精与诚者。何也。不曰祭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乎。推此而往。可知其致诚之道。而其于一切人事。亦必以祖考所是为是。所非为非。虽于一日之间寤寐之顷。我之精神。得与所谓贤人君子者相感而后得梦。始可以信其不妄而诚也。顷余就鞫狱也。勿论余自分于死。虽亲旧。皆不能期其生也。宋景徽谪在康津。一日。梦其先祖尤斋先生。临而诏之曰。汝勿过忧。吾与老先生。已理于帝所矣。翌日。得北来书。闻诬告者之被刑云。所谓老先生。即余先祖沙溪先生。而二先生。即皆世所尊大贤君子也。余谓景徽素贤。而又笃于奉先之诚。其梦不宜妄矣。而然此宜益勉。而不可遽以自信。况其以余乎。则尤窃有疑焉。余之无恶逆之罪。固天地鬼神之所临质。而然余不肖无状。岂望其先祖先贤之有以冥佑也哉。景徽爱我过。无乃以其所思。自为其梦。如
所思。夜见于梦。人之所思。有诚有妄。有公有私。牧羊之子。或身为王公。如是而见祖考于暗昧之中。从而曰。吾祖为此事。吾祖有此言云尔。则岂足徵也。而况为贤人君子之子孙。其不可易言者。梦也。贤人君子之子孙。未必皆为贤人君子。如其祖考。然后可以祭。可以梦。然须精与诚而已。所谓精与诚者。何也。不曰祭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乎。推此而往。可知其致诚之道。而其于一切人事。亦必以祖考所是为是。所非为非。虽于一日之间寤寐之顷。我之精神。得与所谓贤人君子者相感而后得梦。始可以信其不妄而诚也。顷余就鞫狱也。勿论余自分于死。虽亲旧。皆不能期其生也。宋景徽谪在康津。一日。梦其先祖尤斋先生。临而诏之曰。汝勿过忧。吾与老先生。已理于帝所矣。翌日。得北来书。闻诬告者之被刑云。所谓老先生。即余先祖沙溪先生。而二先生。即皆世所尊大贤君子也。余谓景徽素贤。而又笃于奉先之诚。其梦不宜妄矣。而然此宜益勉。而不可遽以自信。况其以余乎。则尤窃有疑焉。余之无恶逆之罪。固天地鬼神之所临质。而然余不肖无状。岂望其先祖先贤之有以冥佑也哉。景徽爱我过。无乃以其所思。自为其梦。如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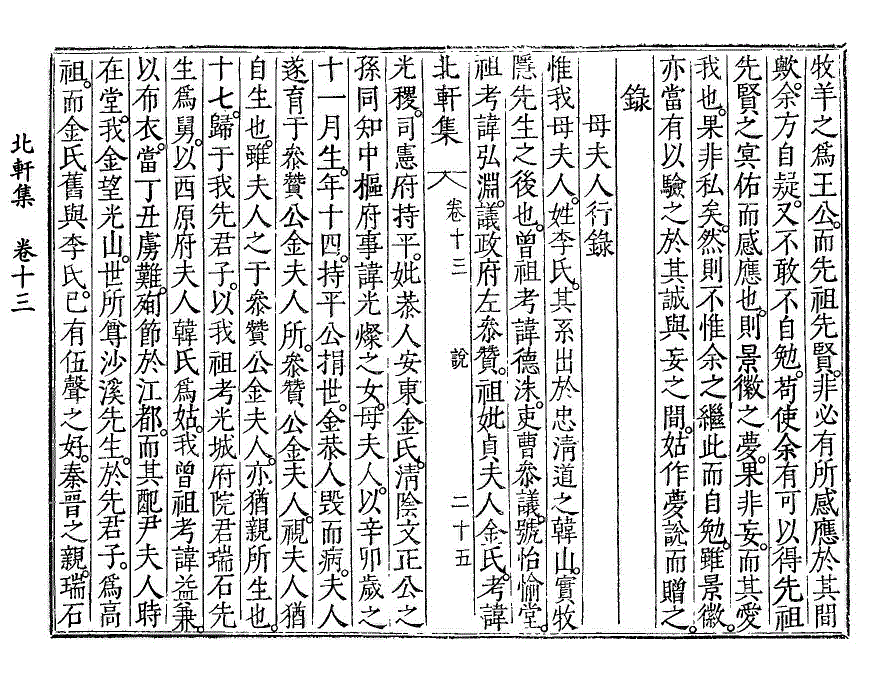 牧羊之为王公。而先祖先贤。非必有所感应于其间欤。余方自疑。又不敢不自勉。苟使余有可以得先祖先贤之冥佑而感应也。则景徽之梦。果非妄。而其爱我也。果非私矣。然则不惟余之继此而自勉。虽景徽。亦当有以验之于其诚与妄之间。姑作梦说而赠之。
牧羊之为王公。而先祖先贤。非必有所感应于其间欤。余方自疑。又不敢不自勉。苟使余有可以得先祖先贤之冥佑而感应也。则景徽之梦。果非妄。而其爱我也。果非私矣。然则不惟余之继此而自勉。虽景徽。亦当有以验之于其诚与妄之间。姑作梦说而赠之。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囚海录(文)○录
母夫人行录
惟我母夫人。姓李氏。其系出于忠清道之韩山。实牧隐先生之后也。曾祖考讳德洙。吏曹参议。号怡愉堂。祖考讳弘渊。议政府左参赞。祖妣贞夫人金氏。考讳光稷。司宪府持平。妣恭人安东金氏。清阴文正公之孙同知中枢府事讳光灿之女。母夫人。以辛卯岁之十一月生。年十四。持平公捐世。金恭人毁而病。夫人遂育于参赞公金夫人所。参赞公金夫人。视夫人犹自生也。虽夫人之于参赞公金夫人。亦犹亲所生也。十七。归于我先君子。以我祖考光城府院君瑞石先生为舅。以西原府夫人韩氏为姑。我曾祖考讳益兼。以布衣。当丁丑虏难。殉节于江都。而其配尹夫人时在堂。我金望光山。世所尊沙溪先生。于先君子。为高祖。而金氏旧与李氏。已有伍声之好。秦晋之亲。瑞石
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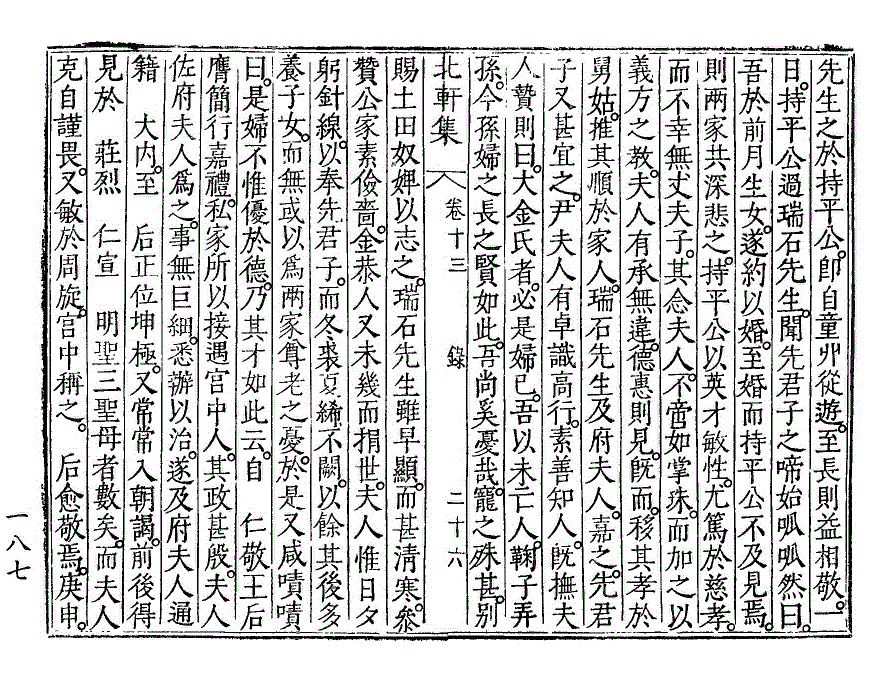 先生之于持平公。即自童丱从游。至长则益相敬。一日。持平公过瑞石先生。闻先君子之啼始呱呱然曰。吾于前月生女。遂约以婚。至婚而持平公不及见焉。则两家共深悲之。持平公以英才敏性。尤笃于慈孝。而不幸无丈夫子。其念夫人。不啻如掌珠。而加之以义方之教。夫人有承无违。德惠则见。既而。移其孝于舅姑。推其顺于家人。瑞石先生及府夫人。嘉之。先君子又甚宜之。尹夫人有卓识高行。素善知人。既抚夫人贽则曰。大金氏者。必是妇已。吾以未亡人。鞠子弄孙。今孙妇之长之贤如此。吾尚奚忧哉。宠之殊甚。别赐土田奴婢以志之。瑞石先生虽早显。而甚清寒。参赞公家素俭啬。金恭人又未几而捐世。夫人惟日夕躬针线。以奉先君子。而冬裘夏絺不阙。以馀其后多养子女。而无或以为两家尊老之忧。于是又咸啧啧曰。是妇不惟优于德。乃其才如此云。自 仁敬王后膺简行嘉礼。私家所以接遇宫中人。其政甚殷。夫人佐府夫人为之。事无巨细。悉办以治。遂及府夫人通籍 大内。至 后正位坤极。又常常入朝谒。前后得见于 庄烈 仁宣 明圣三圣母者数矣。而夫人克自谨畏。又敏于周旋。宫中称之。 后愈敬焉。庚申。
先生之于持平公。即自童丱从游。至长则益相敬。一日。持平公过瑞石先生。闻先君子之啼始呱呱然曰。吾于前月生女。遂约以婚。至婚而持平公不及见焉。则两家共深悲之。持平公以英才敏性。尤笃于慈孝。而不幸无丈夫子。其念夫人。不啻如掌珠。而加之以义方之教。夫人有承无违。德惠则见。既而。移其孝于舅姑。推其顺于家人。瑞石先生及府夫人。嘉之。先君子又甚宜之。尹夫人有卓识高行。素善知人。既抚夫人贽则曰。大金氏者。必是妇已。吾以未亡人。鞠子弄孙。今孙妇之长之贤如此。吾尚奚忧哉。宠之殊甚。别赐土田奴婢以志之。瑞石先生虽早显。而甚清寒。参赞公家素俭啬。金恭人又未几而捐世。夫人惟日夕躬针线。以奉先君子。而冬裘夏絺不阙。以馀其后多养子女。而无或以为两家尊老之忧。于是又咸啧啧曰。是妇不惟优于德。乃其才如此云。自 仁敬王后膺简行嘉礼。私家所以接遇宫中人。其政甚殷。夫人佐府夫人为之。事无巨细。悉办以治。遂及府夫人通籍 大内。至 后正位坤极。又常常入朝谒。前后得见于 庄烈 仁宣 明圣三圣母者数矣。而夫人克自谨畏。又敏于周旋。宫中称之。 后愈敬焉。庚申。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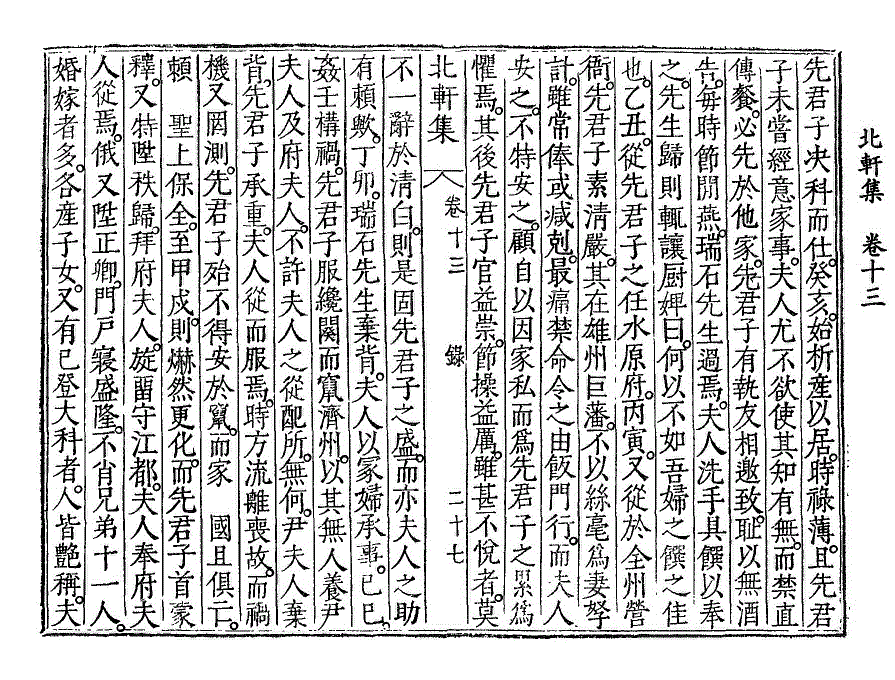 先君子决科而仕。癸亥。始析产以居。时禄薄。且先君子未尝经意家事。夫人尤不欲使其知有无。而禁直传餐。必先于他家。先君子有执友相邀致。耻以无酒告。每时节閒燕。瑞石先生过焉。夫人洗手具馔以奉之。先生归则辄让厨婢曰。何以不如吾妇之馔之佳也。乙丑。从先君子之任水原府。丙寅。又从于全州营衙。先君子素清严。其在雄州巨藩。不以丝毫为妻孥计。虽常俸或减剋。最痛禁命令之由饭门行。而夫人安之。不特安之。顾自以因家私而为先君子之累为惧焉。其后先君子官益崇。节操益厉。虽甚不悦者。莫不一辞于清白。则是固先君子之盛。而亦夫人之助有赖欤。丁卯。瑞石先生弃背。夫人以冢妇承事。己巳。奸壬构祸。先君子服才阕而窜济州。以其无人养尹夫人及府夫人。不许夫人之从配所。无何。尹夫人弃背。先君子承重。夫人从而服焉。时方流离丧故。而祸机又罔测。先君子殆不得安于窜。而家 国且俱亡。赖 圣上保全。至甲戌。则赫然更化。而先君子首蒙释。又特升秩归。拜府夫人。旋留守江都。夫人奉府夫人从焉。俄又升正卿。门户寝盛隆。不肖兄弟十一人。婚嫁者多。各产子女。又有已登大科者。人皆艳称。夫
先君子决科而仕。癸亥。始析产以居。时禄薄。且先君子未尝经意家事。夫人尤不欲使其知有无。而禁直传餐。必先于他家。先君子有执友相邀致。耻以无酒告。每时节閒燕。瑞石先生过焉。夫人洗手具馔以奉之。先生归则辄让厨婢曰。何以不如吾妇之馔之佳也。乙丑。从先君子之任水原府。丙寅。又从于全州营衙。先君子素清严。其在雄州巨藩。不以丝毫为妻孥计。虽常俸或减剋。最痛禁命令之由饭门行。而夫人安之。不特安之。顾自以因家私而为先君子之累为惧焉。其后先君子官益崇。节操益厉。虽甚不悦者。莫不一辞于清白。则是固先君子之盛。而亦夫人之助有赖欤。丁卯。瑞石先生弃背。夫人以冢妇承事。己巳。奸壬构祸。先君子服才阕而窜济州。以其无人养尹夫人及府夫人。不许夫人之从配所。无何。尹夫人弃背。先君子承重。夫人从而服焉。时方流离丧故。而祸机又罔测。先君子殆不得安于窜。而家 国且俱亡。赖 圣上保全。至甲戌。则赫然更化。而先君子首蒙释。又特升秩归。拜府夫人。旋留守江都。夫人奉府夫人从焉。俄又升正卿。门户寝盛隆。不肖兄弟十一人。婚嫁者多。各产子女。又有已登大科者。人皆艳称。夫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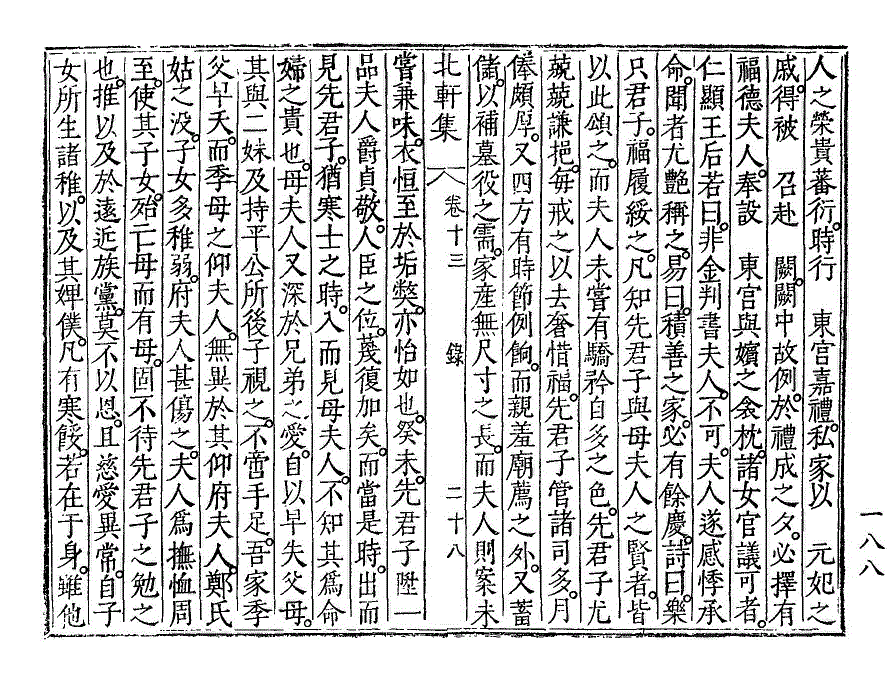 人之荣贵蕃衍。时行 东宫嘉礼。私家以 元妃之戚。得被 召赴 阙。阙中故例。于礼成之夕。必择有福德夫人。奉设 东宫与嫔之衾枕。诸女官议可者。仁显王后若曰。非金判书夫人。不可。夫人遂感悸承命。闻者尤艳称之。易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凡知先君子与母夫人之贤者。皆以此颂之。而夫人未尝有骄矜自多之色。先君子尤兢兢谦挹。每戒之以去奢惜福。先君子管诸司多。月俸颇厚。又四方有时节例饷。而亲羞庙荐之外。又蓄储。以补墓役之需。家产无尺寸之长。而夫人则案未尝兼味。衣恒至于垢弊。亦怡如也。癸未。先君子升一品夫人爵贞敬。人臣之位。蔑复加矣。而当是时。出而见先君子。犹寒士之时。入而见母夫人。不知其为命妇之贵也。母夫人又深于兄弟之爱。自以早失父母。其与二妹及持平公所后子视之。不啻手足。吾家季父早夭。而季母之仰夫人。无异于其仰府夫人。郑氏姑之没。子女多稚弱。府夫人甚伤之。夫人为抚恤周至。使其子女。殆亡母而有母。固不待先君子之勉之也。推以及于远近族党。莫不以恩。且慈爱异常。自子女所生诸稚。以及其婢仆。凡有寒馁。若在于身。虽他
人之荣贵蕃衍。时行 东宫嘉礼。私家以 元妃之戚。得被 召赴 阙。阙中故例。于礼成之夕。必择有福德夫人。奉设 东宫与嫔之衾枕。诸女官议可者。仁显王后若曰。非金判书夫人。不可。夫人遂感悸承命。闻者尤艳称之。易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凡知先君子与母夫人之贤者。皆以此颂之。而夫人未尝有骄矜自多之色。先君子尤兢兢谦挹。每戒之以去奢惜福。先君子管诸司多。月俸颇厚。又四方有时节例饷。而亲羞庙荐之外。又蓄储。以补墓役之需。家产无尺寸之长。而夫人则案未尝兼味。衣恒至于垢弊。亦怡如也。癸未。先君子升一品夫人爵贞敬。人臣之位。蔑复加矣。而当是时。出而见先君子。犹寒士之时。入而见母夫人。不知其为命妇之贵也。母夫人又深于兄弟之爱。自以早失父母。其与二妹及持平公所后子视之。不啻手足。吾家季父早夭。而季母之仰夫人。无异于其仰府夫人。郑氏姑之没。子女多稚弱。府夫人甚伤之。夫人为抚恤周至。使其子女。殆亡母而有母。固不待先君子之勉之也。推以及于远近族党。莫不以恩。且慈爱异常。自子女所生诸稚。以及其婢仆。凡有寒馁。若在于身。虽他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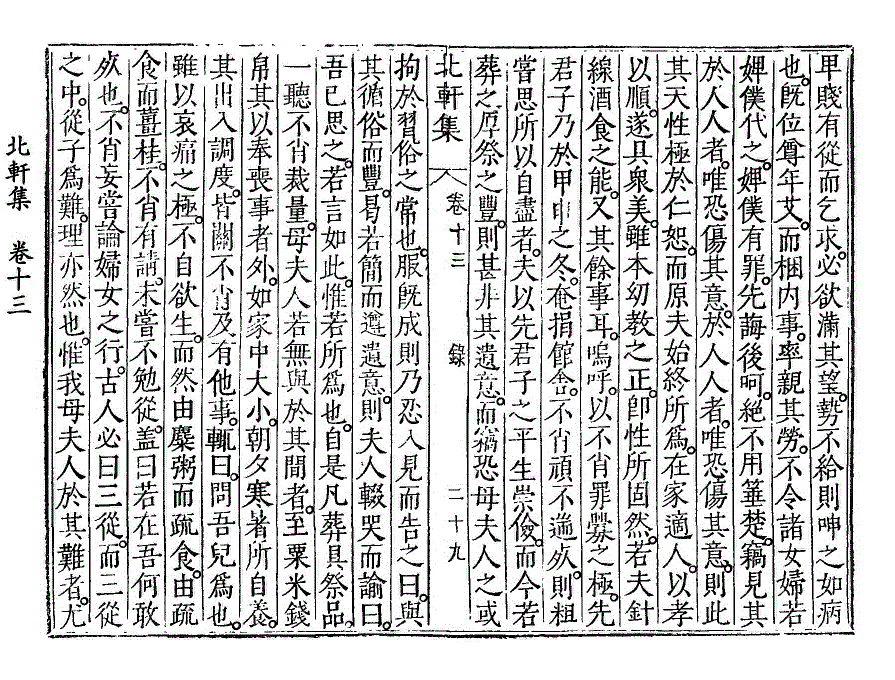 卑贱有从而乞求。必欲满其望。势不给则呻之如病也。既位尊年艾。而梱内事。率亲其劳。不令诸女妇若婢仆代之。婢仆有罪。先诲后呵。绝不用箠楚。窃见其于人人者。唯恐伤其意。于人人者。唯恐伤其意。则此其天性极于仁恕。而原夫始终所为。在家适人。以孝以顺。遂具众美。虽本幼教之正。即性所固然。若夫针线酒食之能。又其馀事耳。呜呼。以不肖罪衅之极。先君子乃于甲申之冬。奄捐馆舍。不肖顽不遄死。则粗尝思所以自尽者。夫以先君子之平生崇俭。而今若葬之厚祭之丰。则甚非其遗意。而窃恐母夫人之或拘于习俗之常也。服既成则乃忍入见而告之曰。与其循俗而丰。曷若简而遵遗意。则夫人辍哭而谕曰。吾已思之。若言如此。惟若所为也。自是凡葬具祭品。一听不肖裁量。母夫人若无与于其间者。至粟米钱帛其以奉丧事者外。如家中大小。朝夕寒暑所自养。其出入调度。皆关不肖及有他事。辄曰。问吾儿为也。虽以哀痛之极。不自欲生。而然由麋粥而疏食。由疏食而姜桂。不肖有请。未尝不勉从。盖曰若在吾何敢死也。不肖妄尝论妇女之行。古人必曰三从。而三从之中。从子为难。理亦然也。惟我母夫人于其难者。尤
卑贱有从而乞求。必欲满其望。势不给则呻之如病也。既位尊年艾。而梱内事。率亲其劳。不令诸女妇若婢仆代之。婢仆有罪。先诲后呵。绝不用箠楚。窃见其于人人者。唯恐伤其意。于人人者。唯恐伤其意。则此其天性极于仁恕。而原夫始终所为。在家适人。以孝以顺。遂具众美。虽本幼教之正。即性所固然。若夫针线酒食之能。又其馀事耳。呜呼。以不肖罪衅之极。先君子乃于甲申之冬。奄捐馆舍。不肖顽不遄死。则粗尝思所以自尽者。夫以先君子之平生崇俭。而今若葬之厚祭之丰。则甚非其遗意。而窃恐母夫人之或拘于习俗之常也。服既成则乃忍入见而告之曰。与其循俗而丰。曷若简而遵遗意。则夫人辍哭而谕曰。吾已思之。若言如此。惟若所为也。自是凡葬具祭品。一听不肖裁量。母夫人若无与于其间者。至粟米钱帛其以奉丧事者外。如家中大小。朝夕寒暑所自养。其出入调度。皆关不肖及有他事。辄曰。问吾儿为也。虽以哀痛之极。不自欲生。而然由麋粥而疏食。由疏食而姜桂。不肖有请。未尝不勉从。盖曰若在吾何敢死也。不肖妄尝论妇女之行。古人必曰三从。而三从之中。从子为难。理亦然也。惟我母夫人于其难者。尤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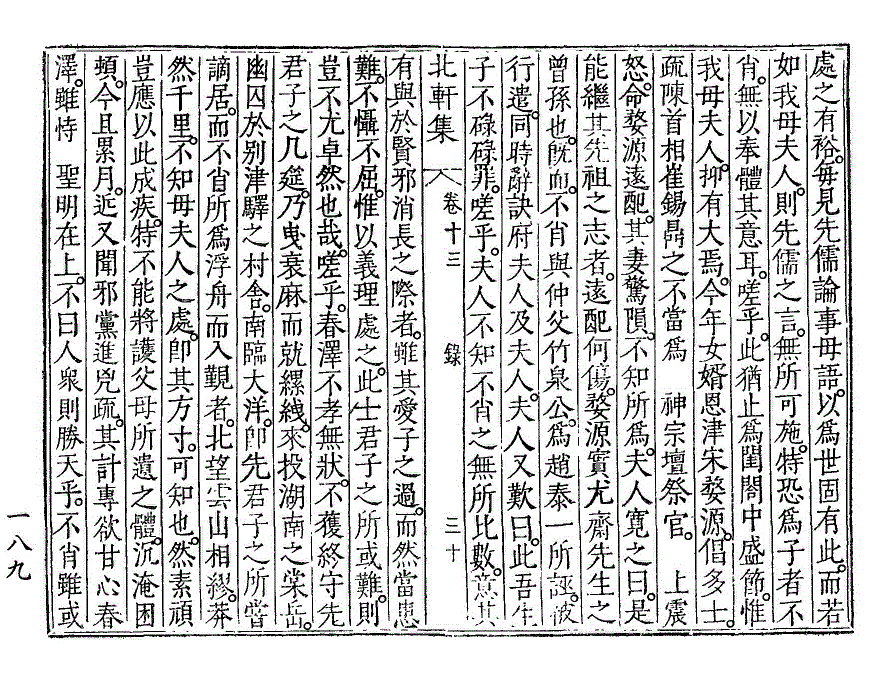 处之有裕。每见先儒论事母语。以为世固有此。而若如我母夫人。则先儒之言。无所可施。特恐为子者不肖。无以奉体其意耳。嗟乎。此犹止为闺閤中盛节。惟我母夫人。抑有大焉。今年女婿恩津宋婺源。倡多士。疏陈首相崔锡鼎之不当为 神宗坛祭官。 上震怒。命婺源远配。其妻惊陨。不知所为。夫人宽之曰。是能继其先祖之志者。远配何伤。婺源实尤斋先生之曾孙也。既而。不肖与仲父竹泉公。为赵泰一所诬。被行遣。同时辞诀府夫人及夫人。夫人又叹曰。此吾生子不碌碌罪。嗟乎。夫人不知不肖之无所比数。意其有与于贤邪消长之际者。虽其爱子之过。而然当患难。不慑不屈。惟以义理处之。此士君子之所或难。则岂不尤卓然也哉。嗟乎。春泽不孝无状。不获终守先君子之几筵。乃曳衰麻而就缧绁。来投湖南之棠岳。幽囚于别津驿之村舍。南临大洋。即先君子之所尝谪居。而不肖所为浮舟而入觐者。北望云山相缪。莽然千里。不知母夫人之处。即其方寸。可知也。然素顽岂应以此成疾。特不能将护父母所遗之体。沉淹困顿。今且累月。近又闻邪党进凶疏。其计专欲甘心春泽。虽恃 圣明在上。不曰人众则胜天乎。不肖虽或
处之有裕。每见先儒论事母语。以为世固有此。而若如我母夫人。则先儒之言。无所可施。特恐为子者不肖。无以奉体其意耳。嗟乎。此犹止为闺閤中盛节。惟我母夫人。抑有大焉。今年女婿恩津宋婺源。倡多士。疏陈首相崔锡鼎之不当为 神宗坛祭官。 上震怒。命婺源远配。其妻惊陨。不知所为。夫人宽之曰。是能继其先祖之志者。远配何伤。婺源实尤斋先生之曾孙也。既而。不肖与仲父竹泉公。为赵泰一所诬。被行遣。同时辞诀府夫人及夫人。夫人又叹曰。此吾生子不碌碌罪。嗟乎。夫人不知不肖之无所比数。意其有与于贤邪消长之际者。虽其爱子之过。而然当患难。不慑不屈。惟以义理处之。此士君子之所或难。则岂不尤卓然也哉。嗟乎。春泽不孝无状。不获终守先君子之几筵。乃曳衰麻而就缧绁。来投湖南之棠岳。幽囚于别津驿之村舍。南临大洋。即先君子之所尝谪居。而不肖所为浮舟而入觐者。北望云山相缪。莽然千里。不知母夫人之处。即其方寸。可知也。然素顽岂应以此成疾。特不能将护父母所遗之体。沉淹困顿。今且累月。近又闻邪党进凶疏。其计专欲甘心春泽。虽恃 圣明在上。不曰人众则胜天乎。不肖虽或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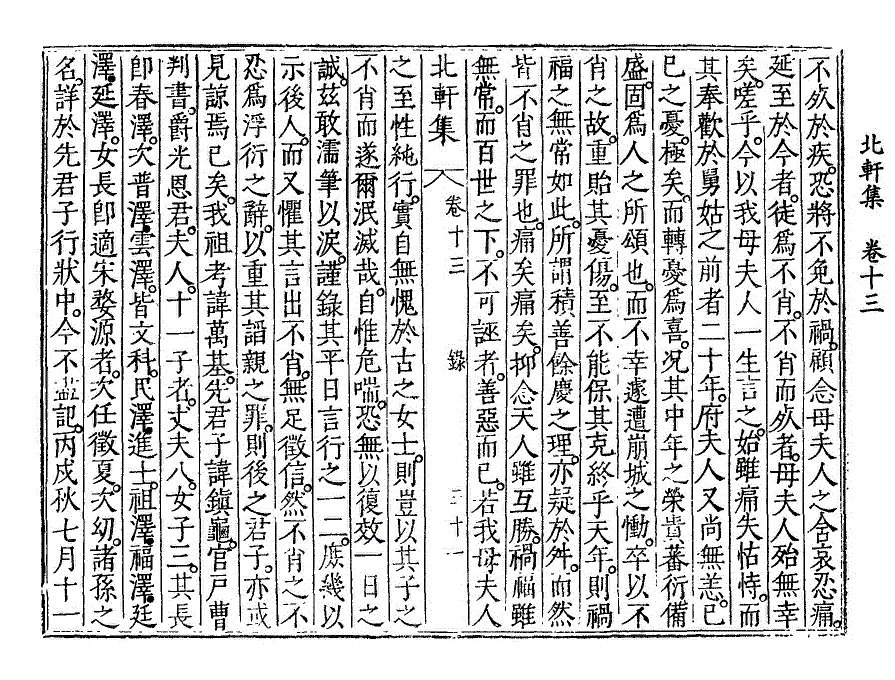 不死于疾。恐将不免于祸。顾念母夫人之含哀忍痛。延至于今者。徒为不肖。不肖而死者。母夫人殆无幸矣。嗟乎。今以我母夫人一生言之。始虽痛失怙恃。而其奉欢于舅姑之前者二十年。府夫人又尚无恙。己巳之忧。极矣。而转忧为喜。况其中年之荣贵蕃衍备盛。固为人之所颂也。而不幸遽遭崩城之恸。卒以不肖之故。重贻其忧伤。至不能保其克终乎天年。则祸福之无常如此。所谓积善馀庆之理。亦疑于舛。而然皆不肖之罪也。痛矣痛矣。抑念天人虽互胜。祸福虽无常。而百世之下。不可诬者。善恶而已。若我母夫人之至性纯行。实自无愧于古之女士。则岂以其子之不肖而遂尔泯灭哉。自惟危喘。恐无以复效一日之诚。玆敢濡笔以泪。谨录其平日言行之一二。庶几以示后人。而又惧其言出不肖。无足徵信。然不肖之不忍为浮衍之辞。以重其谄亲之罪。则后之君子。亦或见谅焉已矣。我祖考讳万基。先君子讳镇龟。官户曹判书。爵光恩君。夫人。十一子者。丈夫八。女子三。其长即春泽。次普泽,云泽。皆文科。民泽,进士。祖泽,福泽,廷泽,延泽。女长即适宋婺源者。次任徵夏。次幼。诸孙之名。详于先君子行状中。今不尽记。丙戌秋七月十一
不死于疾。恐将不免于祸。顾念母夫人之含哀忍痛。延至于今者。徒为不肖。不肖而死者。母夫人殆无幸矣。嗟乎。今以我母夫人一生言之。始虽痛失怙恃。而其奉欢于舅姑之前者二十年。府夫人又尚无恙。己巳之忧。极矣。而转忧为喜。况其中年之荣贵蕃衍备盛。固为人之所颂也。而不幸遽遭崩城之恸。卒以不肖之故。重贻其忧伤。至不能保其克终乎天年。则祸福之无常如此。所谓积善馀庆之理。亦疑于舛。而然皆不肖之罪也。痛矣痛矣。抑念天人虽互胜。祸福虽无常。而百世之下。不可诬者。善恶而已。若我母夫人之至性纯行。实自无愧于古之女士。则岂以其子之不肖而遂尔泯灭哉。自惟危喘。恐无以复效一日之诚。玆敢濡笔以泪。谨录其平日言行之一二。庶几以示后人。而又惧其言出不肖。无足徵信。然不肖之不忍为浮衍之辞。以重其谄亲之罪。则后之君子。亦或见谅焉已矣。我祖考讳万基。先君子讳镇龟。官户曹判书。爵光恩君。夫人。十一子者。丈夫八。女子三。其长即春泽。次普泽,云泽。皆文科。民泽,进士。祖泽,福泽,廷泽,延泽。女长即适宋婺源者。次任徵夏。次幼。诸孙之名。详于先君子行状中。今不尽记。丙戌秋七月十一北轩居士集卷之十三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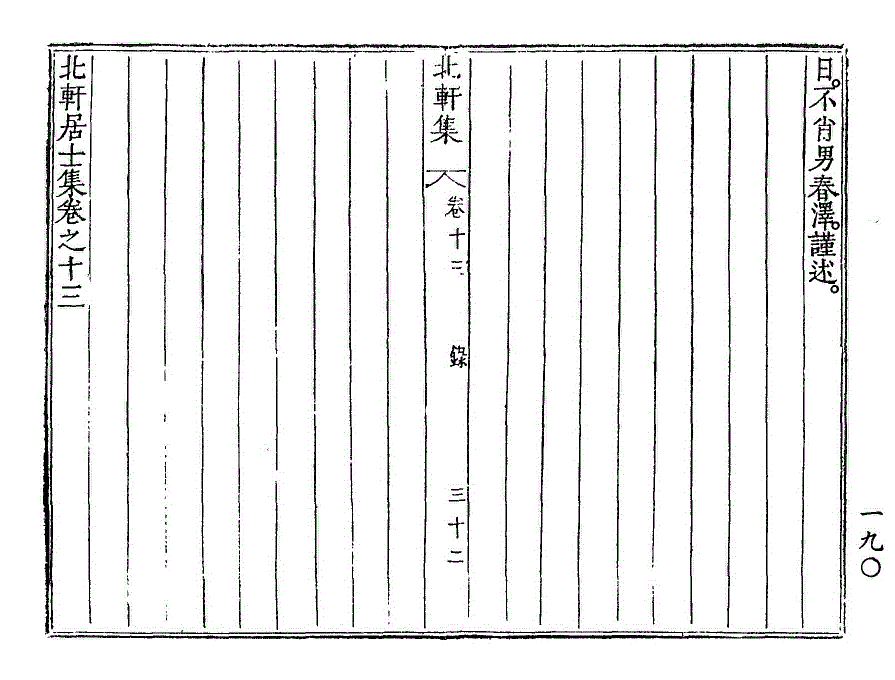 日。不肖男春泽。谨述。
日。不肖男春泽。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