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x 页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初年录(文)○史论
初年录(文)○史论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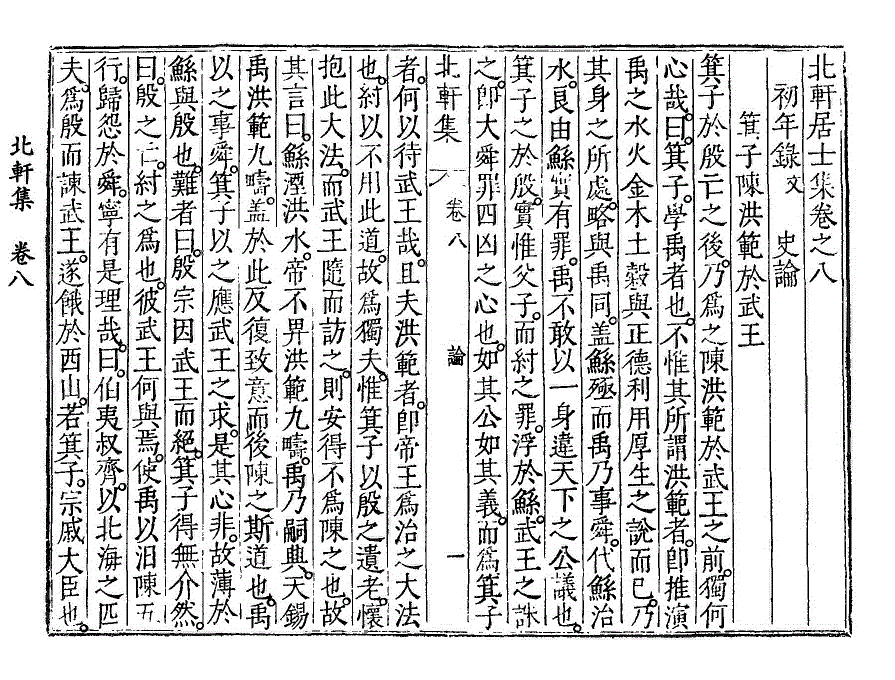 箕子陈洪范于武王
箕子陈洪范于武王箕子于殷亡之后。乃为之陈洪范于武王之前。独何心哉。曰。箕子。学禹者也。不惟其所谓洪范者。即推演禹之水火金木土谷与正德利用厚生之说而已。乃其身之所处。略与禹同。盖鲧殛而禹乃事舜。代鲧治水。良由鲧实有罪。禹不敢以一身违天下之公议也。箕子之于殷。实惟父子。而纣之罪。浮于鲧。武王之诛之。即大舜罪四凶之心也。如其公如其义。而为箕子者。何以待武王哉。且夫洪范者。即帝王为治之大法也。纣以不用此道。故为独夫。惟箕子以殷之遗老。怀抱此大法。而武王随而访之。则安得不为陈之也。故其言曰。鲧湮洪水。帝不畀洪范九畴。禹乃嗣兴。天锡禹洪范九畴。盖于此反复致意而后陈之斯道也。禹以之事舜。箕子以之应武王之求。是其心非。故薄于鲧与殷也。难者曰。殷宗因武王而绝。箕子得无介然。曰。殷之亡。纣之为也。彼武王何与焉。使禹以汩陈五行。归怨于舜。宁有是理哉。曰。伯夷叔齐。以北海之匹夫。为殷而谏武王。遂饿于西山。若箕子。宗戚大臣也。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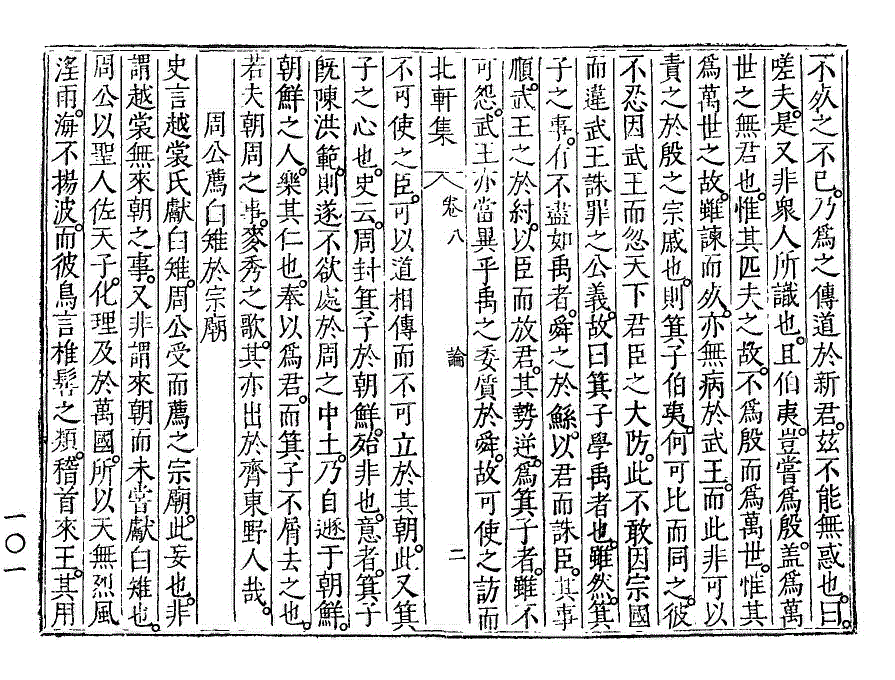 不死之不已。乃为之传道于新君。玆不能无惑也。曰。嗟夫。是又非众人所识也。且伯夷。岂尝为殷。盖为万世之无君也。惟其匹夫之故。不为殷而为万世。惟其为万世之故。虽谏而死。亦无病于武王。而此非可以责之于殷之宗戚也。则箕子伯夷。何可比而同之。彼不忍因武王而忽天下君臣之大防。此不敢因宗国而违武王诛罪之公义。故曰箕子学禹者也。虽然。箕子之事。有不尽如禹者。舜之于鲧。以君而诛臣。其事顺。武王之于纣。以臣而放君。其势逆。为箕子者。虽不可怨。武王亦当异乎禹之委质于舜。故可使之访而不可使之臣。可以道相传而不可立于其朝。此又箕子之心也。史云。周封箕子于朝鲜。殆非也。意者。箕子既陈洪范。则遂不欲处于周之中土。乃自遁于朝鲜。朝鲜之人。乐其仁也。奉以为君。而箕子不屑去之也。若夫朝周之事。麦秀之歌。其亦出于齐东野人哉。
不死之不已。乃为之传道于新君。玆不能无惑也。曰。嗟夫。是又非众人所识也。且伯夷。岂尝为殷。盖为万世之无君也。惟其匹夫之故。不为殷而为万世。惟其为万世之故。虽谏而死。亦无病于武王。而此非可以责之于殷之宗戚也。则箕子伯夷。何可比而同之。彼不忍因武王而忽天下君臣之大防。此不敢因宗国而违武王诛罪之公义。故曰箕子学禹者也。虽然。箕子之事。有不尽如禹者。舜之于鲧。以君而诛臣。其事顺。武王之于纣。以臣而放君。其势逆。为箕子者。虽不可怨。武王亦当异乎禹之委质于舜。故可使之访而不可使之臣。可以道相传而不可立于其朝。此又箕子之心也。史云。周封箕子于朝鲜。殆非也。意者。箕子既陈洪范。则遂不欲处于周之中土。乃自遁于朝鲜。朝鲜之人。乐其仁也。奉以为君。而箕子不屑去之也。若夫朝周之事。麦秀之歌。其亦出于齐东野人哉。周公荐白雉于宗庙
史言越裳氏献白雉。周公受而荐之宗庙。此妄也。非谓越裳无来朝之事。又非谓来朝而未尝献白雉也。周公以圣人佐天子。化理及于万国。所以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而彼鸟言椎髻之类。稽首来王。其用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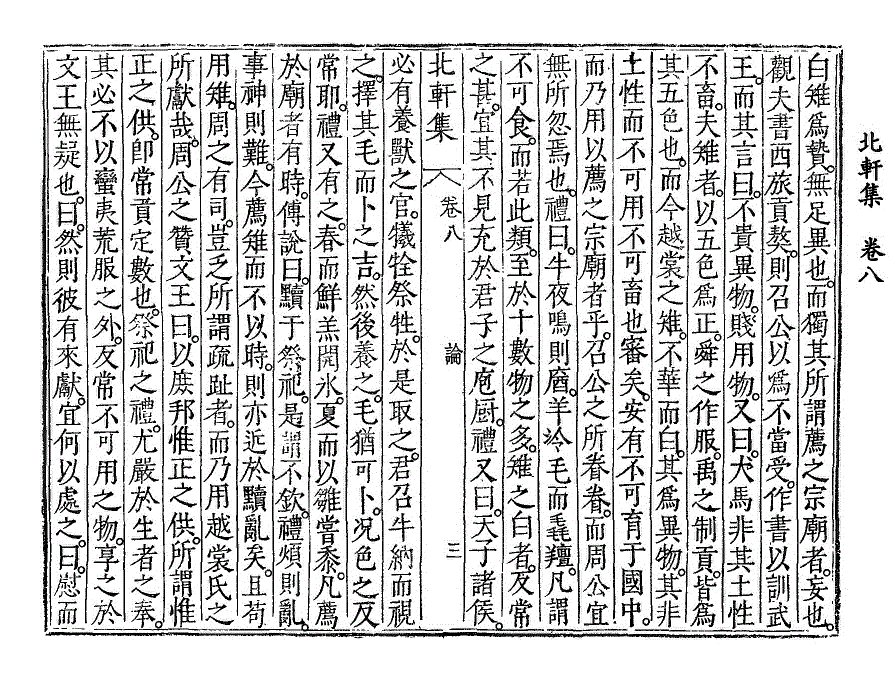 白雉为贽。无足异也。而独其所谓荐之宗庙者。妄也。观夫书西旅贡獒。则召公以为不当受。作书以训武王。而其言曰。不贵异物。贱用物。又曰。犬马非其土性不畜。夫雉者。以五色为正。舜之作服。禹之制贡。皆为其五色也。而今越裳之雉。不华而白。其为异物。其非土性而不可用不可畜也审矣。安有不可育于国中。而乃用以荐之宗庙者乎。召公之所眷眷。而周公宜无所忽焉也。礼曰。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凡谓不可食。而若此类。至于十数物之多。雉之白者。反常之甚。宜其不见充于君子之庖厨。礼又曰。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牺牷祭牲。于是取之。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毛犹可卜。况色之反常耶。礼又有之。春而鲜羔开冰。夏而以雏尝黍。凡荐于庙者有时。傅说曰。黩于祭祀。是谓不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今荐雉而不以时。则亦近于黩乱矣。且苟用雉。周之有司。岂乏所谓疏趾者。而乃用越裳氏之所献哉。周公之赞文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所谓惟正之供。即常贡定数也。祭祀之礼。尤严于生者之奉。其必不以蛮夷荒服之外。反常不可用之物。享之于文王无疑也。曰。然则彼有来献。宜何以处之。曰。慰而
白雉为贽。无足异也。而独其所谓荐之宗庙者。妄也。观夫书西旅贡獒。则召公以为不当受。作书以训武王。而其言曰。不贵异物。贱用物。又曰。犬马非其土性不畜。夫雉者。以五色为正。舜之作服。禹之制贡。皆为其五色也。而今越裳之雉。不华而白。其为异物。其非土性而不可用不可畜也审矣。安有不可育于国中。而乃用以荐之宗庙者乎。召公之所眷眷。而周公宜无所忽焉也。礼曰。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凡谓不可食。而若此类。至于十数物之多。雉之白者。反常之甚。宜其不见充于君子之庖厨。礼又曰。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牺牷祭牲。于是取之。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毛犹可卜。况色之反常耶。礼又有之。春而鲜羔开冰。夏而以雏尝黍。凡荐于庙者有时。傅说曰。黩于祭祀。是谓不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今荐雉而不以时。则亦近于黩乱矣。且苟用雉。周之有司。岂乏所谓疏趾者。而乃用越裳氏之所献哉。周公之赞文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所谓惟正之供。即常贡定数也。祭祀之礼。尤严于生者之奉。其必不以蛮夷荒服之外。反常不可用之物。享之于文王无疑也。曰。然则彼有来献。宜何以处之。曰。慰而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2L 页
 抚之。资而遣之。还其所献可也。受而放诸山林。犹善于荐之也。直以远方之人。怀慕中国之化。执土物而来贡。其物又反常焉。则视为旷绝可贵之事。谓周公成王。必不敢独享。故荐之宗庙。有若归美告成。然而遂有此妄说。史氏不察。以误后人。凡荒君佞臣矫诬矜大。欲以惑人之视听者。未必不藉口于此。如汉武之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作为歌诗。协于宗庙。亦一事也。
抚之。资而遣之。还其所献可也。受而放诸山林。犹善于荐之也。直以远方之人。怀慕中国之化。执土物而来贡。其物又反常焉。则视为旷绝可贵之事。谓周公成王。必不敢独享。故荐之宗庙。有若归美告成。然而遂有此妄说。史氏不察。以误后人。凡荒君佞臣矫诬矜大。欲以惑人之视听者。未必不藉口于此。如汉武之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作为歌诗。协于宗庙。亦一事也。荀息,里克是非。
晋献公疾。召大夫荀息。托其子奚齐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稽首而对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献公卒。奚齐立。中大夫里克杀之。荀息立奚齐之弟卓。里克弑之及荀息。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杜元凯以为荀息有诗人重言之义。司马氏谓献公废长立少。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遽以死许之。是荀息之言。玷于献公未没之前。左氏之志所以贬荀息也。春秋书曰。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谷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胡氏引其说于传。至如苏氏。又以为因国人之所欲废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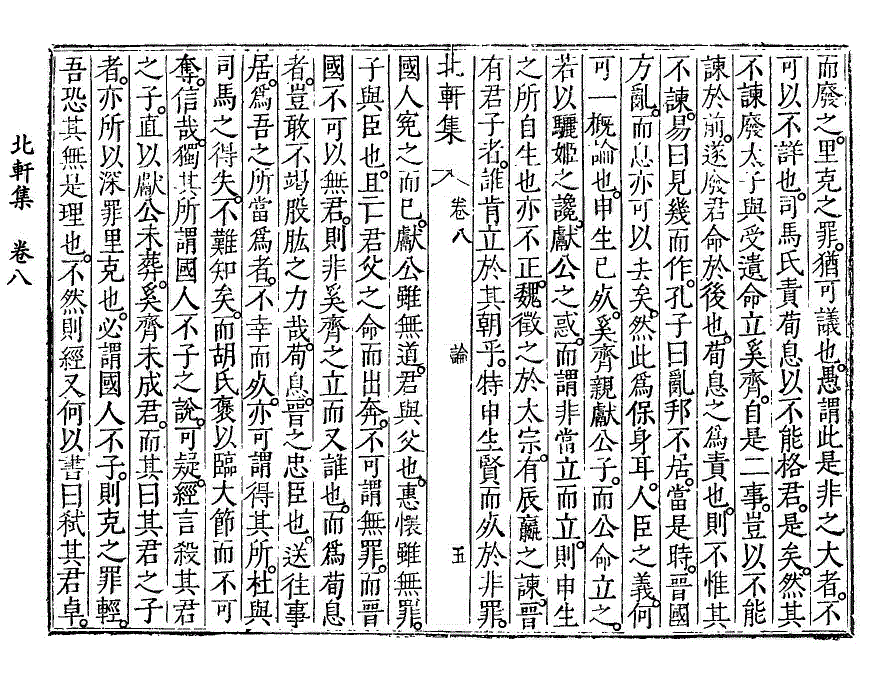 而废之。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愚谓此是非之大者。不可以不详也。司马氏责荀息以不能格君。是矣。然其不谏废太子与受遗命立奚齐。自是二事。岂以不能谏于前。遂废君命于后也。荀息之为责也。则不惟其不谏。易曰见几而作。孔子曰乱邦不居。当是时。晋国方乱。而息亦可以去矣。然此为保身耳。人臣之义。何可一概论也。申生已死。奚齐亲献公子。而公命立之。若以骊姬之谗。献公之惑。而谓非当立而立。则申生之所自生也亦不正。魏徵之于太宗。有辰嬴之谏。晋有君子者。谁肯立于其朝乎。特申生贤而死于非罪。国人冤之而已。献公虽无道。君与父也。惠怀虽无罪。子与臣也。且亡君父之命而出奔。不可谓无罪。而晋国不可以无君。则非奚齐之立而又谁也。而为荀息者。岂敢不竭股肱之力哉。荀息。晋之忠臣也。送往事居。为吾之所当为者。不幸而死。亦可谓得其所。杜与司马之得失。不难知矣。而胡氏褒以临大节而不可夺。信哉。独其所谓国人不子之说。可疑。经言杀其君之子。直以献公未葬。奚齐未成君。而其曰其君之子者。亦所以深罪里克也。必谓国人不子。则克之罪轻。吾恐其无是理也。不然则经又何以书曰弑其君卓。
而废之。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愚谓此是非之大者。不可以不详也。司马氏责荀息以不能格君。是矣。然其不谏废太子与受遗命立奚齐。自是二事。岂以不能谏于前。遂废君命于后也。荀息之为责也。则不惟其不谏。易曰见几而作。孔子曰乱邦不居。当是时。晋国方乱。而息亦可以去矣。然此为保身耳。人臣之义。何可一概论也。申生已死。奚齐亲献公子。而公命立之。若以骊姬之谗。献公之惑。而谓非当立而立。则申生之所自生也亦不正。魏徵之于太宗。有辰嬴之谏。晋有君子者。谁肯立于其朝乎。特申生贤而死于非罪。国人冤之而已。献公虽无道。君与父也。惠怀虽无罪。子与臣也。且亡君父之命而出奔。不可谓无罪。而晋国不可以无君。则非奚齐之立而又谁也。而为荀息者。岂敢不竭股肱之力哉。荀息。晋之忠臣也。送往事居。为吾之所当为者。不幸而死。亦可谓得其所。杜与司马之得失。不难知矣。而胡氏褒以临大节而不可夺。信哉。独其所谓国人不子之说。可疑。经言杀其君之子。直以献公未葬。奚齐未成君。而其曰其君之子者。亦所以深罪里克也。必谓国人不子。则克之罪轻。吾恐其无是理也。不然则经又何以书曰弑其君卓。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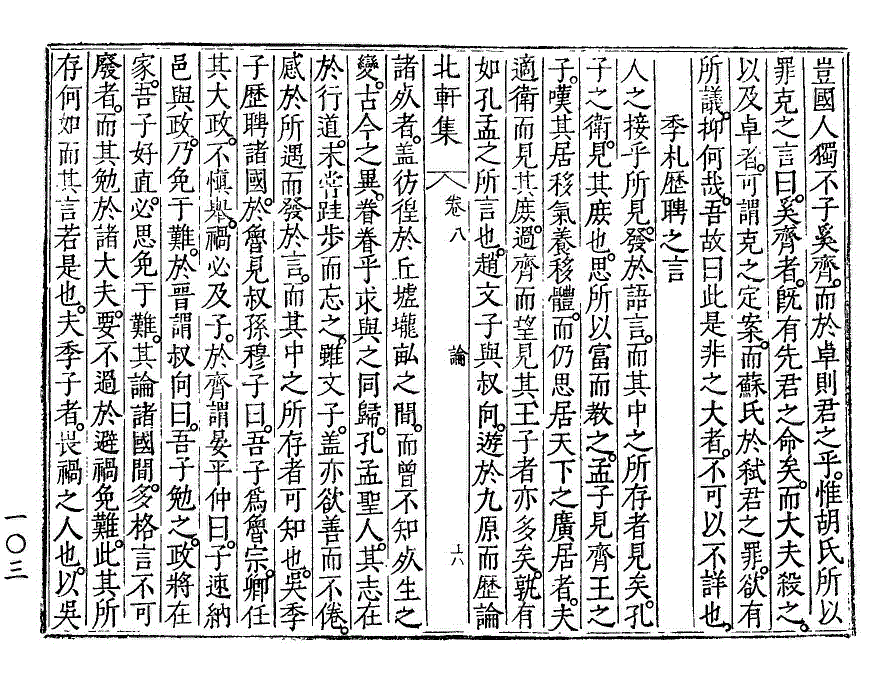 岂国人独不子奚齐。而于卓则君之乎。惟胡氏所以罪克之言曰。奚齐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杀之。以及卓者。可谓克之定案。而苏氏于弑君之罪。欲有所议。抑何哉。吾故曰此是非之大者。不可以不详也。
岂国人独不子奚齐。而于卓则君之乎。惟胡氏所以罪克之言曰。奚齐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杀之。以及卓者。可谓克之定案。而苏氏于弑君之罪。欲有所议。抑何哉。吾故曰此是非之大者。不可以不详也。季札历聘之言
人之接乎所见。发于语言。而其中之所存者见矣。孔子之卫。见其庶也。思所以富而教之。孟子见齐王之子。叹其居移气养移体。而仍思居天下之广居者。夫适卫而见其庶。过齐而望见其王子者亦多矣。孰有如孔孟之所言也。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而历论诸死者。盖彷徨于丘墟垄亩之间。而曾不知死生之变。古今之异。眷眷乎求与之同归。孔孟圣人。其志在于行道。未尝跬步而忘之。虽文子。盖亦欲善而不倦。感于所遇而发于言。而其中之所存者可知也。吴季子历聘诸国。于鲁见叔孙穆子曰。吾子为鲁宗。卿任其大政。不慎举。祸必及子。于齐谓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乃免于难。于晋谓叔向曰。吾子勉之。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免于难。其论诸国间。多格言不可废者。而其勉于诸大夫。要不过于避祸免难。此其所存何如而其言若是也。夫季子者。畏祸之人也。以吴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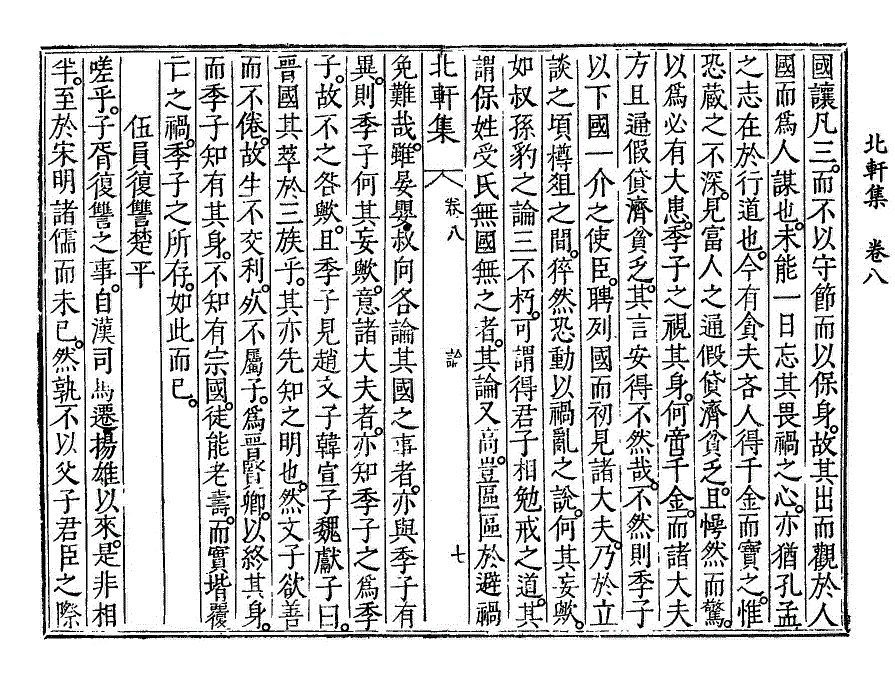 国让凡三。而不以守节而以保身。故其出而观于人国而为人谋也。未能一日忘其畏祸之心。亦犹孔孟之志在于行道也。今有贪夫吝人得千金而宝之。惟恐藏之不深。见富人之通假贷济贫乏。且愕然而惊。以为必有大患。季子之视其身。何啻千金。而诸大夫方且通假贷济贫乏。其言安得不然哉。不然则季子以下国一介之使臣。聘列国而初见诸大夫。乃于立谈之顷樽俎之间。猝然恐动以祸乱之说。何其妄欤。如叔孙豹之论三不朽。可谓得君子相勉戒之道。其谓保姓受氏无国无之者。其论又高。岂区区于避祸免难哉。虽晏婴,叔向各论其国之事者。亦与季子有异。则季子何其妄欤。意诸大夫者。亦知季子之为季子。故不之咎欤。且季子见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其亦先知之明也。然文子欲善而不倦。故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为晋贤卿。以终其身。而季子知有其身。不知有宗国。徒能老寿。而实阶覆亡之祸。季子之所存。如此而已。
国让凡三。而不以守节而以保身。故其出而观于人国而为人谋也。未能一日忘其畏祸之心。亦犹孔孟之志在于行道也。今有贪夫吝人得千金而宝之。惟恐藏之不深。见富人之通假贷济贫乏。且愕然而惊。以为必有大患。季子之视其身。何啻千金。而诸大夫方且通假贷济贫乏。其言安得不然哉。不然则季子以下国一介之使臣。聘列国而初见诸大夫。乃于立谈之顷樽俎之间。猝然恐动以祸乱之说。何其妄欤。如叔孙豹之论三不朽。可谓得君子相勉戒之道。其谓保姓受氏无国无之者。其论又高。岂区区于避祸免难哉。虽晏婴,叔向各论其国之事者。亦与季子有异。则季子何其妄欤。意诸大夫者。亦知季子之为季子。故不之咎欤。且季子见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其亦先知之明也。然文子欲善而不倦。故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为晋贤卿。以终其身。而季子知有其身。不知有宗国。徒能老寿。而实阶覆亡之祸。季子之所存。如此而已。伍员复雠楚平
嗟乎。子胥复雠之事。自汉司马迁,扬雄以来。是非相半。至于宋明诸儒而未已。然孰不以父子君臣之际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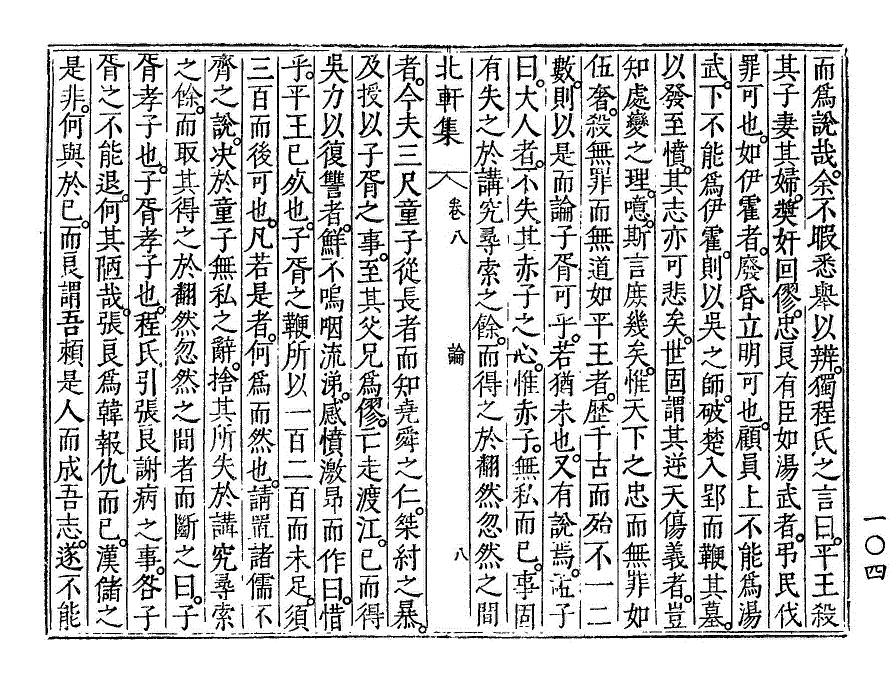 而为说哉。余不暇悉举以辨。独程氏之言曰。平王杀其子妻其妇。奖奸回僇。忠良有臣如汤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废昏立明可也。顾员上不能为汤武。下不能为伊霍。则以吴之师。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发至愤。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谓其逆天伤义者。岂知处变之理。噫。斯言庶几矣。惟天下之忠而无罪如伍奢。杀无罪而无道如平王者。历千古而殆不一二数。则以是而论子胥可乎。若犹未也。又有说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惟赤子。无私而已。事固有失之于讲究寻索之馀。而得之于翻然忽然之间者。今夫三尺童子从长者而知尧舜之仁。桀纣之暴。及授以子胥之事。至其父兄为僇。亡走渡江。已而得吴力以复雠者。鲜不呜咽流涕。感愤激昂而作曰。惜乎。平王已死也。子胥之鞭所以一百二百而未足。须三百而后可也。凡若是者。何为而然也。请置诸儒不齐之说。决于童子无私之辞。舍其所失于讲究寻索之馀。而取其得之于翻然忽然之间者而断之曰。子胥孝子也。子胥孝子也。程氏引张良谢病之事。咎子胥之不能退。何其陋哉。张良为韩报仇而已。汉储之是非。何与于己。而良谓吾赖是人而成吾志。遂不能
而为说哉。余不暇悉举以辨。独程氏之言曰。平王杀其子妻其妇。奖奸回僇。忠良有臣如汤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废昏立明可也。顾员上不能为汤武。下不能为伊霍。则以吴之师。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发至愤。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谓其逆天伤义者。岂知处变之理。噫。斯言庶几矣。惟天下之忠而无罪如伍奢。杀无罪而无道如平王者。历千古而殆不一二数。则以是而论子胥可乎。若犹未也。又有说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惟赤子。无私而已。事固有失之于讲究寻索之馀。而得之于翻然忽然之间者。今夫三尺童子从长者而知尧舜之仁。桀纣之暴。及授以子胥之事。至其父兄为僇。亡走渡江。已而得吴力以复雠者。鲜不呜咽流涕。感愤激昂而作曰。惜乎。平王已死也。子胥之鞭所以一百二百而未足。须三百而后可也。凡若是者。何为而然也。请置诸儒不齐之说。决于童子无私之辞。舍其所失于讲究寻索之馀。而取其得之于翻然忽然之间者而断之曰。子胥孝子也。子胥孝子也。程氏引张良谢病之事。咎子胥之不能退。何其陋哉。张良为韩报仇而已。汉储之是非。何与于己。而良谓吾赖是人而成吾志。遂不能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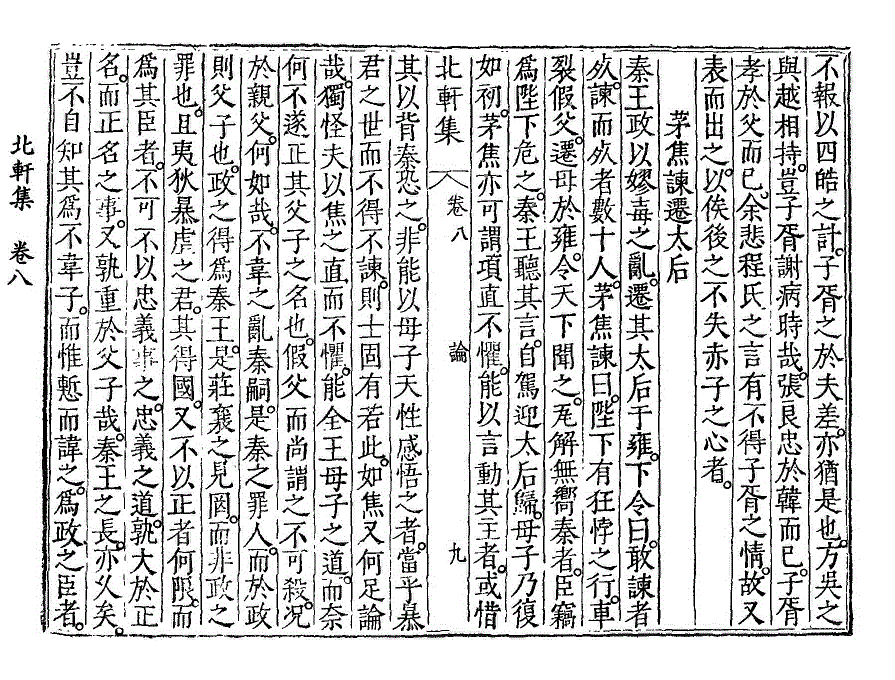 不报以四皓之计。子胥之于夫差。亦犹是也。方吴之与越相持。岂子胥谢病时哉。张良忠于韩而已。子胥孝于父而已。余悲程氏之言有不得子胥之情。故又表而出之。以俟后之不失赤子之心者。
不报以四皓之计。子胥之于夫差。亦犹是也。方吴之与越相持。岂子胥谢病时哉。张良忠于韩而已。子胥孝于父而已。余悲程氏之言有不得子胥之情。故又表而出之。以俟后之不失赤子之心者。茅焦谏迁太后
秦王政以嫪毐之乱。迁其太后于雍。下令曰。敢谏者死。谏而死者数十人。茅焦谏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车裂假父。迁母于雍。令天下闻之。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秦王听其言。自驾迎太后归。母子乃复如初。茅焦亦可谓项直不惧。能以言动其主者。或惜其以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者。当乎暴君之世而不得不谏。则士固有若此。如焦又何足论哉。独怪夫以焦之直而不惧。能全王母子之道。而奈何不遂正其父子之名也。假父而尚谓之不可杀。况于亲父。何如哉。不韦之乱秦嗣。是秦之罪人。而于政则父子也。政之得为秦王。是庄襄之见罔。而非政之罪也。且夷狄暴虐之君。其得国。又不以正者何限。而为其臣者。不可不以忠义事之。忠义之道。孰大于正名。而正名之事。又孰重于父子哉。秦王之长。亦久矣。岂不自知其为不韦子。而惟惭而讳之。为政之臣者。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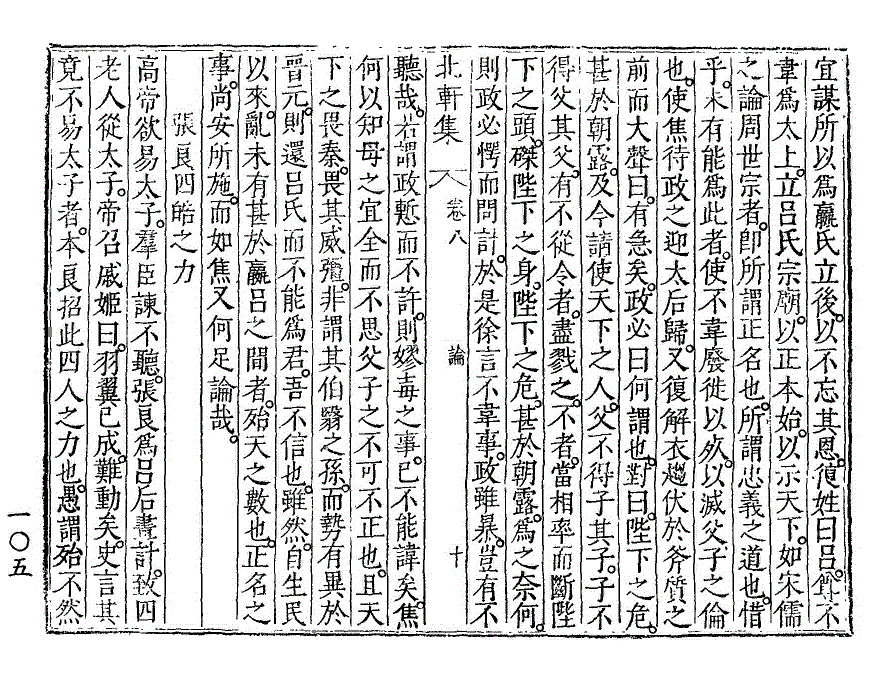 宜谋所以为嬴氏立后。以不忘其恩。复姓曰吕。尊不韦为太上。立吕氏宗庙。以正本始。以示天下。如宋儒之论周世宗者。即所谓正名也。所谓忠义之道也。惜乎。未有能为此者。使不韦废徙以死。以灭父子之伦也。使焦待政之迎太后归。又复解衣趋伏于斧质之前而大声曰。有急矣。政必曰何谓也。对曰。陛下之危。甚于朝露。及今请使天下之人。父不得子其子。子不得父其父。有不从令者。尽戮之。不者。当相率而断陛下之头。磔陛下之身。陛下之危。甚于朝露。为之奈何。则政必愕而问计。于是徐言不韦事。政虽暴。岂有不听哉。若谓政惭而不许。则嫪毐之事。已不能讳矣。焦何以知母之宜全而不思父子之不可不正也。且天下之畏秦。畏其威彊。非谓其伯翳之孙。而势有异于晋元。则还吕氏而不能为君。吾不信也。虽然。自生民以来。乱未有甚于嬴吕之间者。殆天之数也。正名之事。尚安所施。而如焦又何足论哉。
宜谋所以为嬴氏立后。以不忘其恩。复姓曰吕。尊不韦为太上。立吕氏宗庙。以正本始。以示天下。如宋儒之论周世宗者。即所谓正名也。所谓忠义之道也。惜乎。未有能为此者。使不韦废徙以死。以灭父子之伦也。使焦待政之迎太后归。又复解衣趋伏于斧质之前而大声曰。有急矣。政必曰何谓也。对曰。陛下之危。甚于朝露。及今请使天下之人。父不得子其子。子不得父其父。有不从令者。尽戮之。不者。当相率而断陛下之头。磔陛下之身。陛下之危。甚于朝露。为之奈何。则政必愕而问计。于是徐言不韦事。政虽暴。岂有不听哉。若谓政惭而不许。则嫪毐之事。已不能讳矣。焦何以知母之宜全而不思父子之不可不正也。且天下之畏秦。畏其威彊。非谓其伯翳之孙。而势有异于晋元。则还吕氏而不能为君。吾不信也。虽然。自生民以来。乱未有甚于嬴吕之间者。殆天之数也。正名之事。尚安所施。而如焦又何足论哉。张良四皓之力
高帝欲易太子。群臣谏不听。张良为吕后画计。致四老人从太子。帝召戚姬曰。羽翼已成。难动矣。史言其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愚谓殆不然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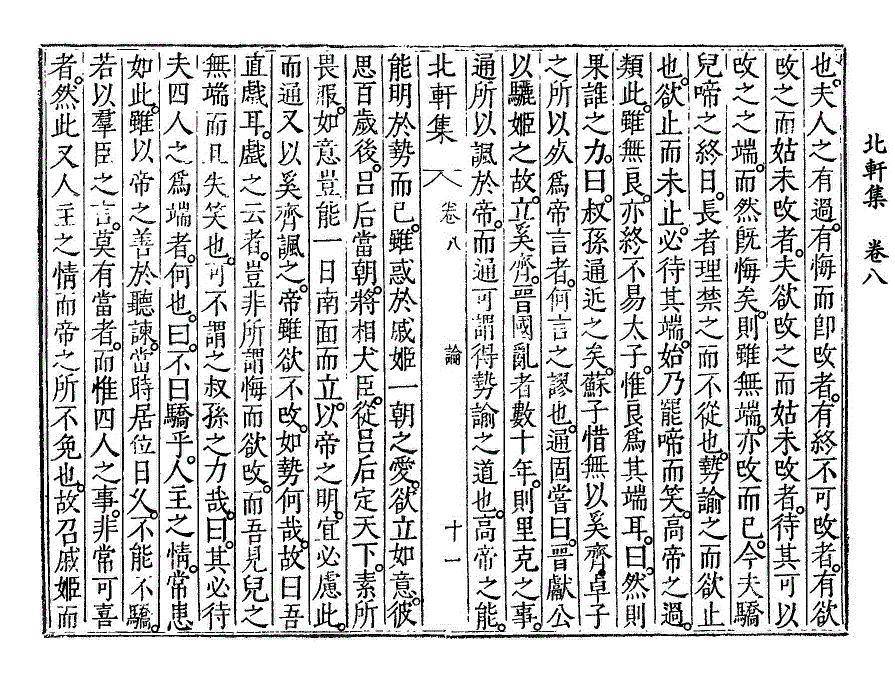 也。夫人之有过。有悔而即改者。有终不可改者。有欲改之而姑未改者。夫欲改之而姑未改者。待其可以改之之端。而然既悔矣。则虽无端。亦改而已。今夫骄儿啼之终日。长者理禁之而不从也。势谕之而欲止也。欲止而未止。必待其端。始乃罢啼而笑。高帝之过。类此。虽无良。亦终不易太子。惟良为其端耳。曰。然则果谁之力。曰。叔孙通近之矣。苏子惜无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帝言者。何言之谬也。通固尝曰。晋献公以骊姬之故。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则里克之事。通所以讽于帝。而通可谓得势谕之道也。高帝之能。能明于势而已。虽惑于戚姬一朝之爱。欲立如意。彼思百岁后。吕后当朝。将相大臣。从吕后定天下。素所畏服。如意岂能一日南面而立。以帝之明。宜必虑此。而通又以奚齐讽之。帝虽欲不改。如势何哉。故曰吾直戏耳。戏之云者。岂非所谓悔而欲改。而吾见儿之无端而且失笑也。可不谓之叔孙之力哉。曰。其必待夫四人之为端者。何也。曰。不曰骄乎。人主之情。常患如此。虽以帝之善于听谏。当时居位日久。不能不骄。若以群臣之言。莫有当者。而惟四人之事。非常可喜者。然此又人主之情而帝之所不免也。故召戚姬而
也。夫人之有过。有悔而即改者。有终不可改者。有欲改之而姑未改者。夫欲改之而姑未改者。待其可以改之之端。而然既悔矣。则虽无端。亦改而已。今夫骄儿啼之终日。长者理禁之而不从也。势谕之而欲止也。欲止而未止。必待其端。始乃罢啼而笑。高帝之过。类此。虽无良。亦终不易太子。惟良为其端耳。曰。然则果谁之力。曰。叔孙通近之矣。苏子惜无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帝言者。何言之谬也。通固尝曰。晋献公以骊姬之故。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则里克之事。通所以讽于帝。而通可谓得势谕之道也。高帝之能。能明于势而已。虽惑于戚姬一朝之爱。欲立如意。彼思百岁后。吕后当朝。将相大臣。从吕后定天下。素所畏服。如意岂能一日南面而立。以帝之明。宜必虑此。而通又以奚齐讽之。帝虽欲不改。如势何哉。故曰吾直戏耳。戏之云者。岂非所谓悔而欲改。而吾见儿之无端而且失笑也。可不谓之叔孙之力哉。曰。其必待夫四人之为端者。何也。曰。不曰骄乎。人主之情。常患如此。虽以帝之善于听谏。当时居位日久。不能不骄。若以群臣之言。莫有当者。而惟四人之事。非常可喜者。然此又人主之情而帝之所不免也。故召戚姬而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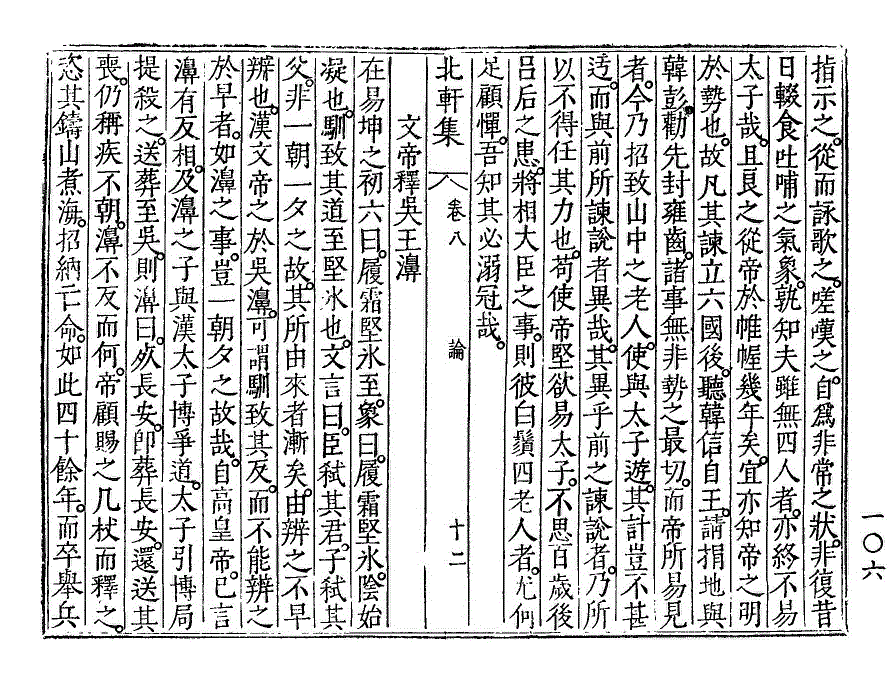 指示之。从而咏歌之。嗟叹之。自为非常之状。非复昔日辍食吐哺之气象。孰知夫虽无四人者。亦终不易太子哉。且良之从帝于帷幄几年矣。宜亦知帝之明于势也。故凡其谏立六国后。听韩信自王。请捐地与韩彭。劝先封雍齿。诸事无非势之最切。而帝所易见者。今乃招致山中之老人。使与太子游。其计岂不甚迂。而与前所谏说者异哉。其异乎前之谏说者。乃所以不得任其力也。苟使帝坚欲易太子。不思百岁后吕后之患。将相大臣之事。则彼白须四老人者。尤何足顾惮。吾知其必溺冠哉。
指示之。从而咏歌之。嗟叹之。自为非常之状。非复昔日辍食吐哺之气象。孰知夫虽无四人者。亦终不易太子哉。且良之从帝于帷幄几年矣。宜亦知帝之明于势也。故凡其谏立六国后。听韩信自王。请捐地与韩彭。劝先封雍齿。诸事无非势之最切。而帝所易见者。今乃招致山中之老人。使与太子游。其计岂不甚迂。而与前所谏说者异哉。其异乎前之谏说者。乃所以不得任其力也。苟使帝坚欲易太子。不思百岁后吕后之患。将相大臣之事。则彼白须四老人者。尤何足顾惮。吾知其必溺冠哉。文帝释吴王濞
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汉文帝之于吴濞。可谓驯致其反。而不能辨之于早者。如濞之事。岂一朝夕之故哉。自高皇帝。已言濞有反相。及濞之子与汉太子博争道。太子引博局提杀之。送葬至吴。则濞曰。死长安。即葬长安。还送其丧。仍称疾不朝。濞不反而何。帝顾赐之几杖而释之。恣其铸山煮海。招纳亡命。如此四十馀年。而卒举兵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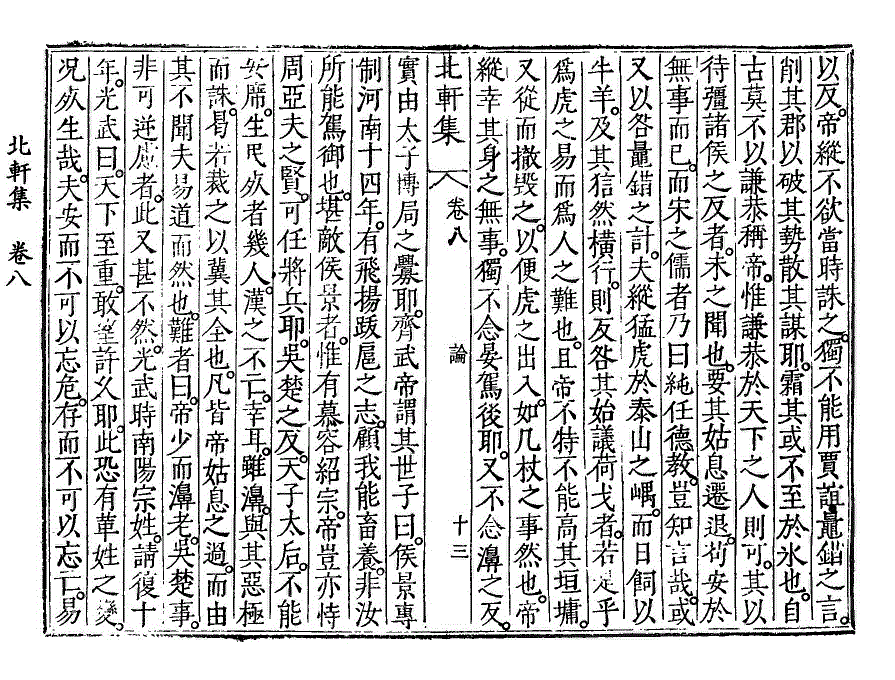 以反。帝纵不欲当时诛之。独不能用贾谊,晁错之言。削其郡以破其势散其谋耶。霜其或不至于冰也。自古莫不以谦恭称帝。惟谦恭于天下之人则可。其以待彊诸侯之反者。未之闻也。要其姑息迁退。苟安于无事而已。而宋之儒者乃曰纯任德教。岂知言哉。或又以咎晁错之计。夫纵猛虎于泰山之嵎。而日饲以牛羊。及其狺然横行。则反咎其始议荷戈者。若是乎为虎之易而为人之难也。且帝不特不能高其垣墉。又从而撤毁之。以便虎之出入。如几杖之事然也。帝纵幸其身之无事。独不念晏驾后耶。又不念濞之反。实由太子博局之衅耶。齐武帝谓其世子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堪敌侯景者。惟有慕容绍宗。帝岂亦恃周亚夫之贤。可任将兵耶。吴楚之反。天子太后。不能安席。生民死者几人。汉之不亡。幸耳。虽濞。与其恶极而诛。曷若裁之以冀其全也。凡皆帝姑息之过。而由其不闻夫易道而然也。难者曰。帝少而濞老。吴楚事。非可逆虑者。此又甚不然。光武时南阳宗姓。请复十年。光武曰。天下至重。敢望许久耶。此恐有革姓之变。况死生哉。夫安而不可以忘危。存而不可以忘亡。易
以反。帝纵不欲当时诛之。独不能用贾谊,晁错之言。削其郡以破其势散其谋耶。霜其或不至于冰也。自古莫不以谦恭称帝。惟谦恭于天下之人则可。其以待彊诸侯之反者。未之闻也。要其姑息迁退。苟安于无事而已。而宋之儒者乃曰纯任德教。岂知言哉。或又以咎晁错之计。夫纵猛虎于泰山之嵎。而日饲以牛羊。及其狺然横行。则反咎其始议荷戈者。若是乎为虎之易而为人之难也。且帝不特不能高其垣墉。又从而撤毁之。以便虎之出入。如几杖之事然也。帝纵幸其身之无事。独不念晏驾后耶。又不念濞之反。实由太子博局之衅耶。齐武帝谓其世子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堪敌侯景者。惟有慕容绍宗。帝岂亦恃周亚夫之贤。可任将兵耶。吴楚之反。天子太后。不能安席。生民死者几人。汉之不亡。幸耳。虽濞。与其恶极而诛。曷若裁之以冀其全也。凡皆帝姑息之过。而由其不闻夫易道而然也。难者曰。帝少而濞老。吴楚事。非可逆虑者。此又甚不然。光武时南阳宗姓。请复十年。光武曰。天下至重。敢望许久耶。此恐有革姓之变。况死生哉。夫安而不可以忘危。存而不可以忘亡。易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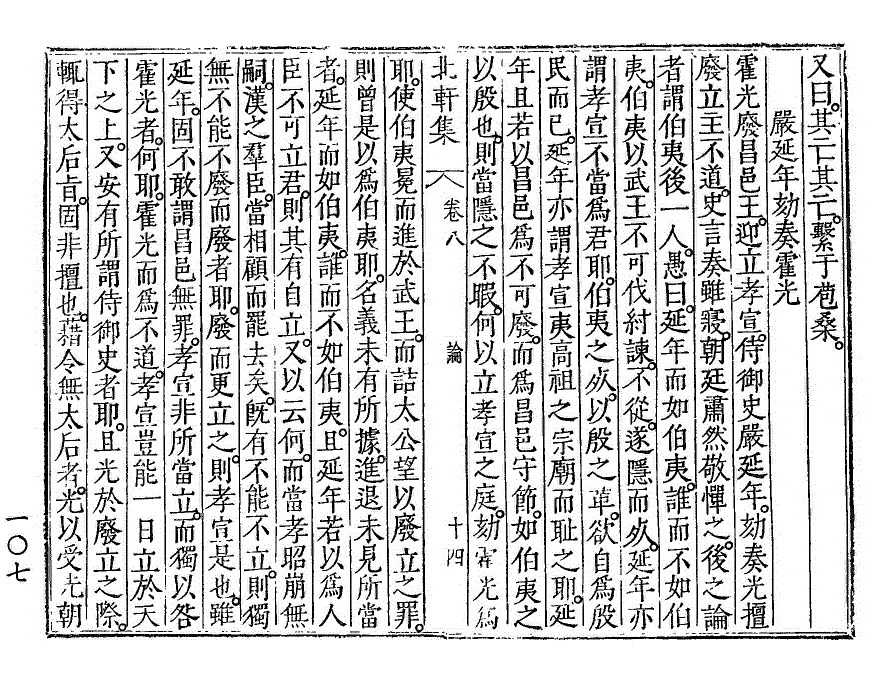 又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又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严延年劾奏霍光
霍光废昌邑王。迎立孝宣。侍御史严延年。劾奏光擅废立主不道。史言奏虽寝。朝廷肃然敬惮之。后之论者谓伯夷后一人。愚曰。延年而如伯夷。谁而不如伯夷。伯夷以武王不可伐纣谏。不从。遂隐而死。延年亦谓孝宣不当为君耶。伯夷之死。以殷之革。欲自为殷民而已。延年亦谓孝宣夷高祖之宗庙而耻之耶。延年且若以昌邑为不可废。而为昌邑守节。如伯夷之以殷也。则当隐之不暇。何以立孝宣之庭。劾霍光为耶。使伯夷冕而进于武王。而诘太公望以废立之罪。则曾是以为伯夷耶。名义未有所据。进退未见所当者。延年而如伯夷。谁而不如伯夷。且延年若以为人臣不可立君。则其有自立。又以云何。而当孝昭崩无嗣。汉之群臣。当相顾而罢去矣。既有不能不立。则独无不能不废而废者耶。废而更立之。则孝宣是也。虽延年。固不敢谓昌邑无罪。孝宣非所当立。而独以咎霍光者。何耶。霍光而为不道。孝宣岂能一日立于天下之上。又安有所谓侍御史者耶。且光于废立之际。辄得太后旨。固非擅也。藉令无太后者。光以受先朝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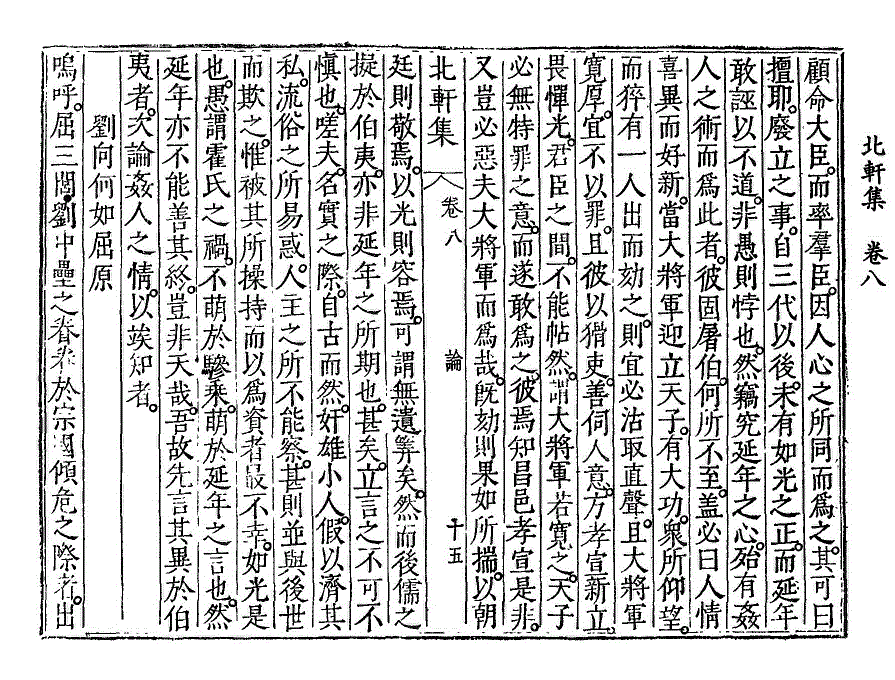 顾命大臣。而率群臣。因人心之所同而为之。其可曰擅耶。废立之事。自三代以后。未有如光之正。而延年敢诬以不道。非愚则悖也。然窃究延年之心。殆有奸人之术而为此者。彼固屠伯。何所不至。盖必曰人情喜异而好新。当大将军迎立天子。有大功。众所仰望。而猝有一人出而劾之。则宜必沽取直声。且大将军宽厚。宜不以罪。且彼以猾吏。善伺人意。方孝宣新立。畏惮光。君臣之间。不能帖然。谓大将军若宽之。天子必无特罪之意。而遂敢为之。彼焉知昌邑孝宣是非。又岂必恶夫大将军而为哉。既劾则果如所揣。以朝廷则敬焉。以光则容焉。可谓无遗算矣。然而后儒之拟于伯夷。亦非延年之所期也。甚矣。立言之不可不慎也。嗟夫。名实之际。自古而然。奸雄小人。假以济其私。流俗之所易惑。人主之所不能察。甚则并与后世而欺之。惟被其所操持而以为资者最不幸。如光是也。愚谓霍氏之祸。不萌于骖乘。萌于延年之言也。然延年亦不能善其终。岂非天哉。吾故先言其异于伯夷者。次论奸人之情。以俟知者。
顾命大臣。而率群臣。因人心之所同而为之。其可曰擅耶。废立之事。自三代以后。未有如光之正。而延年敢诬以不道。非愚则悖也。然窃究延年之心。殆有奸人之术而为此者。彼固屠伯。何所不至。盖必曰人情喜异而好新。当大将军迎立天子。有大功。众所仰望。而猝有一人出而劾之。则宜必沽取直声。且大将军宽厚。宜不以罪。且彼以猾吏。善伺人意。方孝宣新立。畏惮光。君臣之间。不能帖然。谓大将军若宽之。天子必无特罪之意。而遂敢为之。彼焉知昌邑孝宣是非。又岂必恶夫大将军而为哉。既劾则果如所揣。以朝廷则敬焉。以光则容焉。可谓无遗算矣。然而后儒之拟于伯夷。亦非延年之所期也。甚矣。立言之不可不慎也。嗟夫。名实之际。自古而然。奸雄小人。假以济其私。流俗之所易惑。人主之所不能察。甚则并与后世而欺之。惟被其所操持而以为资者最不幸。如光是也。愚谓霍氏之祸。不萌于骖乘。萌于延年之言也。然延年亦不能善其终。岂非天哉。吾故先言其异于伯夷者。次论奸人之情。以俟知者。刘向何如屈原
呜呼。屈三闾,刘中垒之眷眷于宗国倾危之际者。出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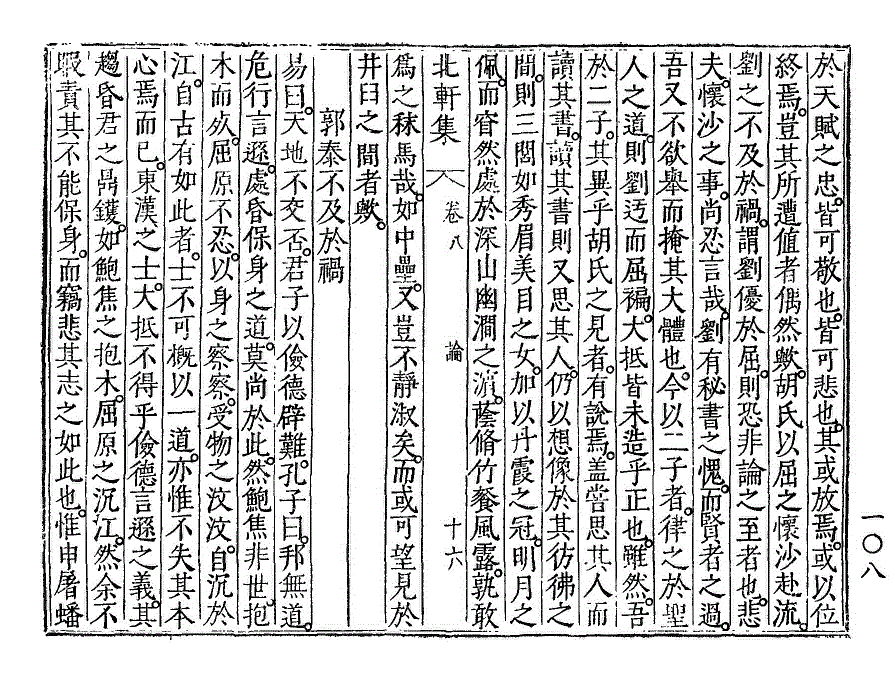 于天赋之忠。皆可敬也。皆可悲也。其或放焉。或以位终焉。岂其所遭值者偶然欤。胡氏以屈之怀沙赴流。刘之不及于祸。谓刘优于屈。则恐非论之至者也。悲夫。怀沙之事。尚忍言哉。刘有秘书之愧。而贤者之过。吾又不欲举而掩其大体也。今以二子者。律之于圣人之道。则刘迂而屈褊。大抵皆未造乎正也。虽然。吾于二子。其异乎胡氏之见者。有说焉。盖尝思其人而读其书。读其书则又思其人。仍以想像于其彷佛之间。则三闾如秀眉美目之女。加以丹霞之冠。明月之佩。而窅然处于深山幽涧之滨。荫脩竹餐风露。孰敢为之秣马哉。如中垒。又岂不静淑矣。而或可望见于井臼之间者欤。
于天赋之忠。皆可敬也。皆可悲也。其或放焉。或以位终焉。岂其所遭值者偶然欤。胡氏以屈之怀沙赴流。刘之不及于祸。谓刘优于屈。则恐非论之至者也。悲夫。怀沙之事。尚忍言哉。刘有秘书之愧。而贤者之过。吾又不欲举而掩其大体也。今以二子者。律之于圣人之道。则刘迂而屈褊。大抵皆未造乎正也。虽然。吾于二子。其异乎胡氏之见者。有说焉。盖尝思其人而读其书。读其书则又思其人。仍以想像于其彷佛之间。则三闾如秀眉美目之女。加以丹霞之冠。明月之佩。而窅然处于深山幽涧之滨。荫脩竹餐风露。孰敢为之秣马哉。如中垒。又岂不静淑矣。而或可望见于井臼之间者欤。郭泰不及于祸
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处昏保身之道。莫尚于此。然鲍焦非世。抱木而死。屈原不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自沉于江。自古有如此者。士不可概以一道。亦惟不失其本心焉而已。东汉之士。大抵不得乎俭德言逊之义。其趋昏君之鼎镬。如鲍焦之抱木。屈原之沉江。然余不暇责其不能保身。而窃悲其志之如此也。惟申屠蟠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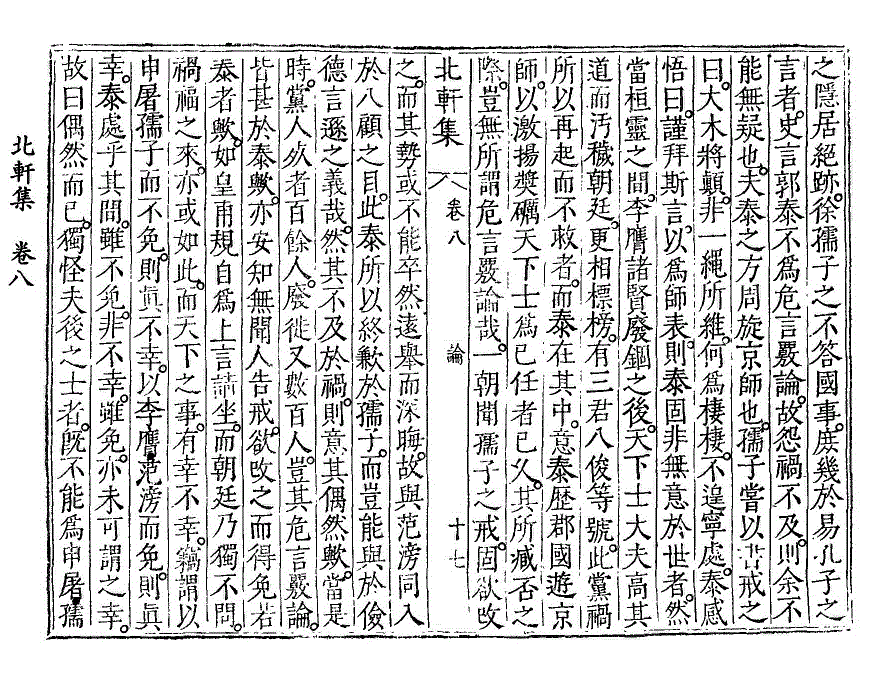 之隐居绝迹。徐孺子之不答国事。庶几于易孔子之言者。史言郭泰不为危言覈论。故怨祸不及。则余不能无疑也。夫泰之方周旋京师也。孺子尝以书戒之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泰感悟曰。谨拜斯言。以为师表。则泰固非无意于世者。然当桓灵之间。李膺诸贤废锢之后。天下士大夫高其道而污秽朝廷。更相标榜。有三君八俊等号。此党祸所以再起而不救者。而泰在其中。意泰历郡国游京师。以激扬奖砺天下士为己任者已久。其所臧否之际。岂无所谓危言覈论哉。一朝闻孺子之戒。固欲改之。而其势或不能卒然远举而深晦。故与范滂同入于八顾之目。此泰所以终歉于孺子。而岂能与于俭德言逊之义哉。然其不及于祸。则意其偶然欤。当是时。党人死者百馀人。废徙又数百人。岂其危言覈论。皆甚于泰欤。亦安知无闻人告戒。欲改之而得免若泰者欤。如皇甫规自为上言请坐。而朝廷乃独不问。祸福之来。亦或如此。而天下之事。有幸不幸。窃谓以申屠孺子而不免。则真不幸。以李膺,范滂而免。则真幸。泰处乎其间。虽不免。非不幸。虽免。亦未可谓之幸。故曰偶然而已。独怪夫后之士者。既不能为申屠,孺
之隐居绝迹。徐孺子之不答国事。庶几于易孔子之言者。史言郭泰不为危言覈论。故怨祸不及。则余不能无疑也。夫泰之方周旋京师也。孺子尝以书戒之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泰感悟曰。谨拜斯言。以为师表。则泰固非无意于世者。然当桓灵之间。李膺诸贤废锢之后。天下士大夫高其道而污秽朝廷。更相标榜。有三君八俊等号。此党祸所以再起而不救者。而泰在其中。意泰历郡国游京师。以激扬奖砺天下士为己任者已久。其所臧否之际。岂无所谓危言覈论哉。一朝闻孺子之戒。固欲改之。而其势或不能卒然远举而深晦。故与范滂同入于八顾之目。此泰所以终歉于孺子。而岂能与于俭德言逊之义哉。然其不及于祸。则意其偶然欤。当是时。党人死者百馀人。废徙又数百人。岂其危言覈论。皆甚于泰欤。亦安知无闻人告戒。欲改之而得免若泰者欤。如皇甫规自为上言请坐。而朝廷乃独不问。祸福之来。亦或如此。而天下之事。有幸不幸。窃谓以申屠孺子而不免。则真不幸。以李膺,范滂而免。则真幸。泰处乎其间。虽不免。非不幸。虽免。亦未可谓之幸。故曰偶然而已。独怪夫后之士者。既不能为申屠,孺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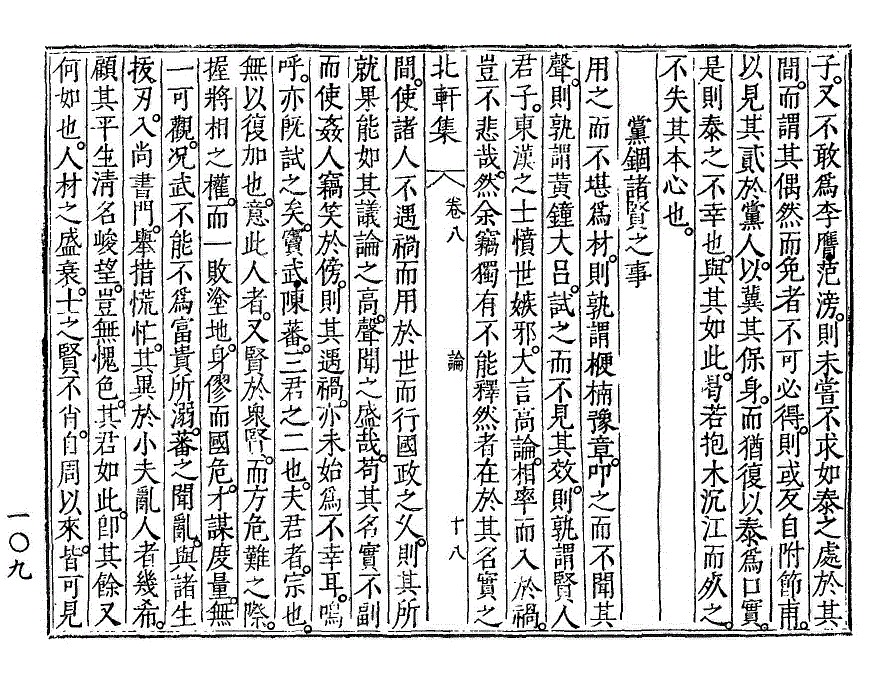 子。又不敢为李膺,范滂。则未尝不求如泰之处于其间。而谓其偶然而免者不可必得。则或反自附节甫。以见其贰于党人。以冀其保身。而犹复以泰为口实。是则泰之不幸也。与其如此。曷若抱木沉江而死之。不失其本心也。
子。又不敢为李膺,范滂。则未尝不求如泰之处于其间。而谓其偶然而免者不可必得。则或反自附节甫。以见其贰于党人。以冀其保身。而犹复以泰为口实。是则泰之不幸也。与其如此。曷若抱木沉江而死之。不失其本心也。党锢诸贤之事
用之而不堪为材。则孰谓楩楠豫章。叩之而不闻其声。则孰谓黄钟大吕。试之而不见其效。则孰谓贤人君子。东汉之士愤世嫉邪。大言高论。相率而入于祸。岂不悲哉。然余窃独有不能释然者在于其名实之间。使诸人不遇祸而用于世而行国政之久。则其所就果能如其议论之高。声闻之盛哉。苟其名实不副而使奸人窃笑于傍。则其遇祸。亦未始为不幸耳。呜呼。亦既试之矣。窦武,陈蕃。三君之二也。夫君者。宗也。无以复加也。意此人者。又贤于众贤。而方危难之际。握将相之权。而一败涂地。身僇而国危。才谋度量。无一可观。况武不能不为富贵所溺。蕃之闻乱。与诸生拔刃。入尚书门。举措慌忙。其异于小夫乱人者几希。顾其平生清名峻望。岂无愧色。其君如此。即其馀又何如也。人材之盛衰。士之贤不肖。自周以来。皆可见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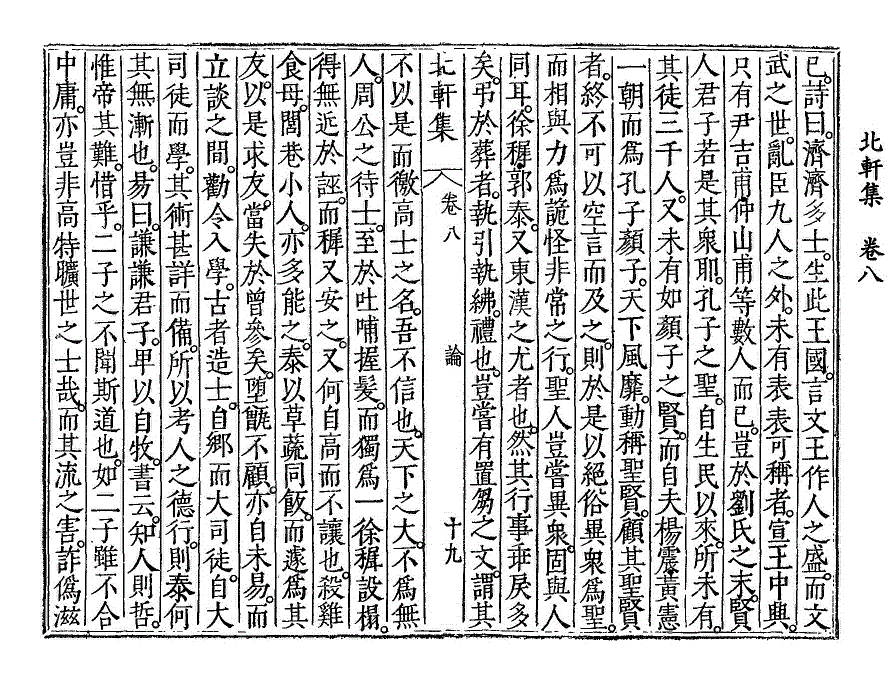 已。诗曰。济济多士。生此王国。言文王作人之盛。而文武之世。乱臣九人之外。未有表表可称者。宣王中兴。只有尹吉甫,仲山甫等数人而已。岂于刘氏之末。贤人君子若是其众耶。孔子之圣。自生民以来。所未有。其徒三千人。又未有如颜子之贤。而自夫杨震,黄宪一朝而为孔子颜子。天下风靡。动称圣贤。顾其圣贤者。终不可以空言而及之。则于是以绝俗异众为圣。而相与力为诡怪非常之行。圣人岂尝异众。固与人同耳。徐稚,郭泰。又东汉之尤者也。然其行事乖戾多矣。吊于葬者。执引执绋。礼也。岂尝有置刍之文。谓其不以是而徼高士之名。吾不信也。天下之大。不为无人。周公之待士。至于吐哺握发。而独为一徐稚设榻。得无近于诬。而稚又安之。又何自高而不让也。杀鸡食母。闾巷小人。亦多能之。泰以草蔬同饭。而遽为其友。以是求友。当失于曾参矣。堕甑不顾。亦自未易。而立谈之间。劝令入学。古者造士。自乡而大司徒。自大司徒而学。其术甚详而备。所以考人之德行。则泰何其无渐也。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书云。知人则哲。惟帝其难。惜乎。二子之不闻斯道也。如二子虽不合中庸。亦岂非高特旷世之士哉。而其流之害。诈伪滋
已。诗曰。济济多士。生此王国。言文王作人之盛。而文武之世。乱臣九人之外。未有表表可称者。宣王中兴。只有尹吉甫,仲山甫等数人而已。岂于刘氏之末。贤人君子若是其众耶。孔子之圣。自生民以来。所未有。其徒三千人。又未有如颜子之贤。而自夫杨震,黄宪一朝而为孔子颜子。天下风靡。动称圣贤。顾其圣贤者。终不可以空言而及之。则于是以绝俗异众为圣。而相与力为诡怪非常之行。圣人岂尝异众。固与人同耳。徐稚,郭泰。又东汉之尤者也。然其行事乖戾多矣。吊于葬者。执引执绋。礼也。岂尝有置刍之文。谓其不以是而徼高士之名。吾不信也。天下之大。不为无人。周公之待士。至于吐哺握发。而独为一徐稚设榻。得无近于诬。而稚又安之。又何自高而不让也。杀鸡食母。闾巷小人。亦多能之。泰以草蔬同饭。而遽为其友。以是求友。当失于曾参矣。堕甑不顾。亦自未易。而立谈之间。劝令入学。古者造士。自乡而大司徒。自大司徒而学。其术甚详而备。所以考人之德行。则泰何其无渐也。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书云。知人则哲。惟帝其难。惜乎。二子之不闻斯道也。如二子虽不合中庸。亦岂非高特旷世之士哉。而其流之害。诈伪滋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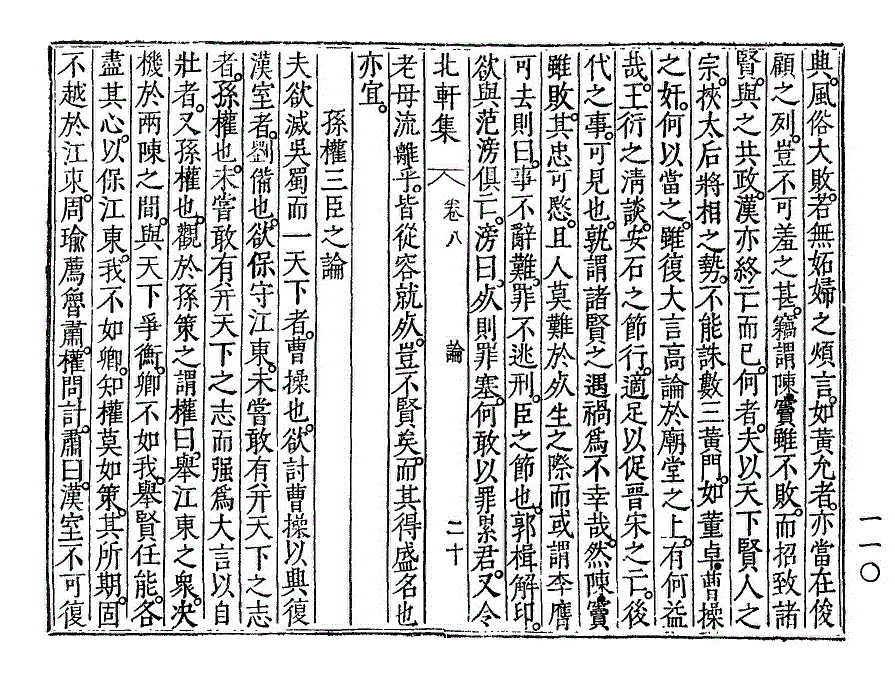 兴。风俗大败。若无妒妇之烦言。如黄允者。亦当在俊顾之列。岂不可羞之甚。窃谓陈,窦虽不败。而招致诸贤。与之共政。汉亦终亡而已。何者。夫以天下贤人之宗。挟太后将相之势。不能诛数三黄门。如董卓,曹操之奸。何以当之。虽复大言高论于庙堂之上。有何益哉。王衍之清谈。安石之节行。适足以促晋宋之亡。后代之事。可见也。孰谓诸贤之遇祸为不幸哉。然陈,窦虽败。其忠可悯。且人莫难于死生之际而或谓李膺可去则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郭楫解印。欲与范滂俱亡。滂曰。死则罪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皆从容就死。岂不贤矣。而其得盛名也亦宜。
兴。风俗大败。若无妒妇之烦言。如黄允者。亦当在俊顾之列。岂不可羞之甚。窃谓陈,窦虽不败。而招致诸贤。与之共政。汉亦终亡而已。何者。夫以天下贤人之宗。挟太后将相之势。不能诛数三黄门。如董卓,曹操之奸。何以当之。虽复大言高论于庙堂之上。有何益哉。王衍之清谈。安石之节行。适足以促晋宋之亡。后代之事。可见也。孰谓诸贤之遇祸为不幸哉。然陈,窦虽败。其忠可悯。且人莫难于死生之际而或谓李膺可去则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郭楫解印。欲与范滂俱亡。滂曰。死则罪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皆从容就死。岂不贤矣。而其得盛名也亦宜。孙权三臣之论
夫欲灭吴蜀而一天下者。曹操也。欲讨曹操以兴复汉室者。刘备也。欲保守江东。未尝敢有并天下之志者。孙权也。未尝敢有并天下之志而强为大言以自壮者。又孙权也。观于孙策之谓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知权莫如策。其所期。固不越于江东。周瑜荐鲁肃。权问计。肃曰。汉室不可复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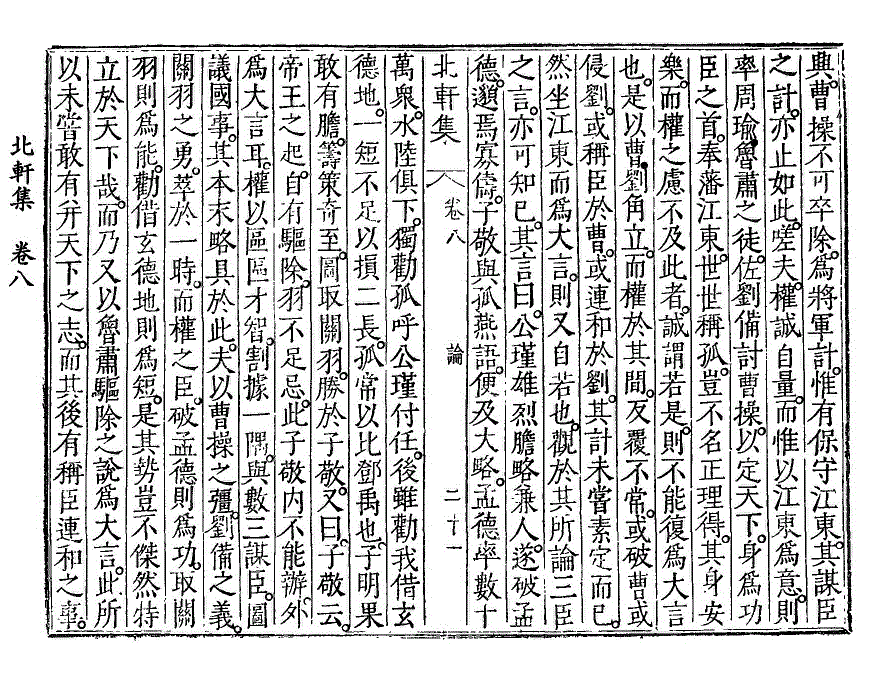 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其谋臣之计。亦止如此。嗟夫。权诚自量。而惟以江东为意。则率周瑜,鲁肃之徒。佐刘备讨曹操。以定天下。身为功臣之首。奉藩江东。世世称孤。岂不名正理得。其身安乐。而权之虑不及此者。诚谓若是。则不能复为大言也。是以曹,刘角立。而权于其间。反覆不常。或破曹或侵刘。或称臣于曹。或连和于刘。其计未尝素定而已。然坐江东而为大言。则又自若也。观于其所论三臣之言。亦可知已。其言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邈焉寡俦。子敬与孤燕语。便及大略。孟德率数十万众。水陆俱下。独劝孤呼公瑾付任。后虽劝我借玄德地。一短不足以损二长。孤常以比邓禹也。子明果敢有胆。筹策奇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又曰。子敬云。帝王之起。自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权以区区才智。割据一隅。与数三谋臣。图议国事。其本末略具于此。夫以曹操之彊。刘备之义。关羽之勇。萃于一时。而权之臣。破孟德则为功。取关羽则为能。劝借玄德地则为短。是其势岂不杰然特立于天下哉。而乃又以鲁肃驱除之说为大言。此所以未尝敢有并天下之志。而其后有称臣连和之事。
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其谋臣之计。亦止如此。嗟夫。权诚自量。而惟以江东为意。则率周瑜,鲁肃之徒。佐刘备讨曹操。以定天下。身为功臣之首。奉藩江东。世世称孤。岂不名正理得。其身安乐。而权之虑不及此者。诚谓若是。则不能复为大言也。是以曹,刘角立。而权于其间。反覆不常。或破曹或侵刘。或称臣于曹。或连和于刘。其计未尝素定而已。然坐江东而为大言。则又自若也。观于其所论三臣之言。亦可知已。其言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邈焉寡俦。子敬与孤燕语。便及大略。孟德率数十万众。水陆俱下。独劝孤呼公瑾付任。后虽劝我借玄德地。一短不足以损二长。孤常以比邓禹也。子明果敢有胆。筹策奇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又曰。子敬云。帝王之起。自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权以区区才智。割据一隅。与数三谋臣。图议国事。其本末略具于此。夫以曹操之彊。刘备之义。关羽之勇。萃于一时。而权之臣。破孟德则为功。取关羽则为能。劝借玄德地则为短。是其势岂不杰然特立于天下哉。而乃又以鲁肃驱除之说为大言。此所以未尝敢有并天下之志。而其后有称臣连和之事。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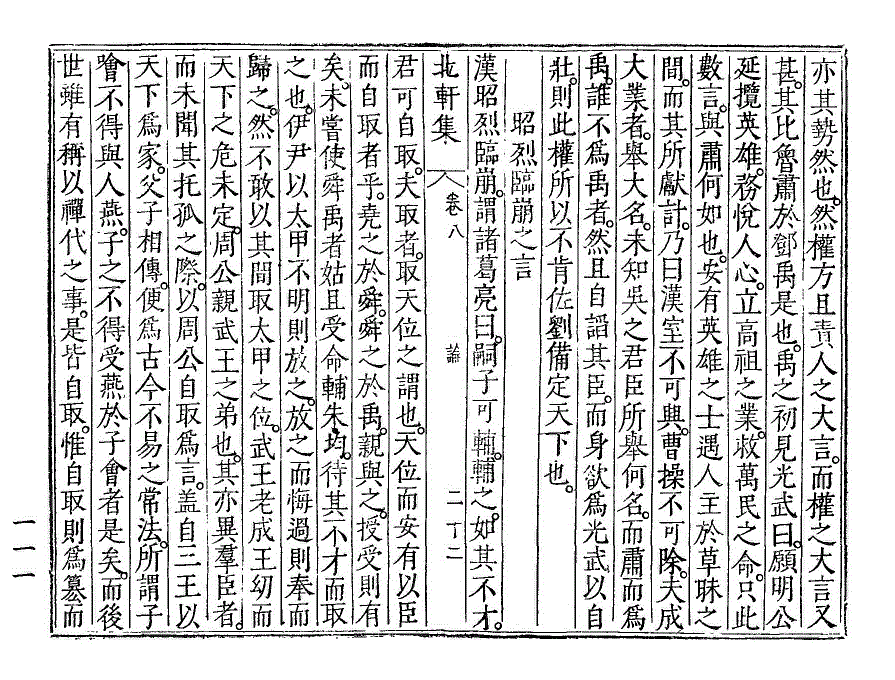 亦其势然也。然权方且责人之大言。而权之大言又甚。其比鲁肃于邓禹是也。禹之初见光武曰。愿明公延揽英雄。务悦人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只此数言。与肃何如也。安有英雄之士遇人主于草昧之间。而其所献计。乃曰汉室不可兴。曹操不可除。夫成大业者。举大名。未知吴之君臣所举何名。而肃而为禹。谁不为禹者。然且自谄其臣。而身欲为光武以自壮。则此权所以不肯佐刘备定天下也。
亦其势然也。然权方且责人之大言。而权之大言又甚。其比鲁肃于邓禹是也。禹之初见光武曰。愿明公延揽英雄。务悦人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只此数言。与肃何如也。安有英雄之士遇人主于草昧之间。而其所献计。乃曰汉室不可兴。曹操不可除。夫成大业者。举大名。未知吴之君臣所举何名。而肃而为禹。谁不为禹者。然且自谄其臣。而身欲为光武以自壮。则此权所以不肯佐刘备定天下也。昭烈临崩之言
汉昭烈临崩。谓诸葛亮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夫取者。取天位之谓也。天位而安有以臣而自取者乎。尧之于舜。舜之于禹。亲与之。授受则有矣。未尝使舜禹者姑且受命辅朱,均。待其不才而取之也。伊尹以太甲不明则放之。放之而悔过则奉而归之。然不敢以其间取太甲之位。武王老成王幼而天下之危未定。周公亲武王之弟也。其亦异群臣者。而未闻其托孤之际。以周公自取为言。盖自三王以天下为家。父子相传。便为古今不易之常法。所谓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会(一作哙)者是矣。而后世虽有称以禅代之事。是皆自取。惟自取则为篡而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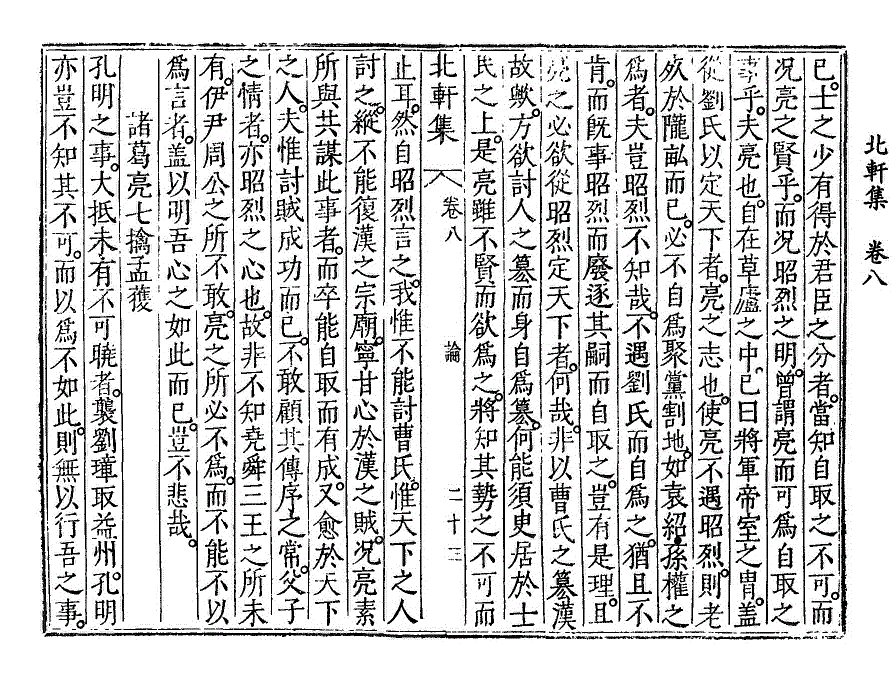 已。士之少有得于君臣之分者。当知自取之不可。而况亮之贤乎。而况昭烈之明。曾谓亮而可为自取之事乎。夫亮也。自在草庐之中。已曰将军帝室之胄。盖从刘氏以定天下者。亮之志也。使亮不遇昭烈。则老死于陇亩而已。必不自为聚党割地。如袁绍,孙权之为者。夫岂昭烈不知哉。不遇刘氏而自为之。犹且不肯。而既事昭烈而废逐其嗣而自取之。岂有是理。且亮之必欲从昭烈定天下者。何哉。非以曹氏之篡汉故欤。方欲讨人之篡而身自为篡。何能须臾居于士民之上。是亮虽不贤而欲为之。将知其势之不可而止耳。然自昭烈言之。我惟不能讨曹氏。惟天下之人讨之。纵不能复汉之宗庙。宁甘心于汉之贼。况亮素所与共谋此事者。而卒能自取而有成。又愈于天下之人。夫惟讨贼成功而已。不敢顾其传序之常。父子之情者。亦昭烈之心也。故非不知尧舜三王之所未有。伊尹周公之所不敢。亮之所必不为。而不能不以为言者。盖以明吾心之如此而已。岂不悲哉。
已。士之少有得于君臣之分者。当知自取之不可。而况亮之贤乎。而况昭烈之明。曾谓亮而可为自取之事乎。夫亮也。自在草庐之中。已曰将军帝室之胄。盖从刘氏以定天下者。亮之志也。使亮不遇昭烈。则老死于陇亩而已。必不自为聚党割地。如袁绍,孙权之为者。夫岂昭烈不知哉。不遇刘氏而自为之。犹且不肯。而既事昭烈而废逐其嗣而自取之。岂有是理。且亮之必欲从昭烈定天下者。何哉。非以曹氏之篡汉故欤。方欲讨人之篡而身自为篡。何能须臾居于士民之上。是亮虽不贤而欲为之。将知其势之不可而止耳。然自昭烈言之。我惟不能讨曹氏。惟天下之人讨之。纵不能复汉之宗庙。宁甘心于汉之贼。况亮素所与共谋此事者。而卒能自取而有成。又愈于天下之人。夫惟讨贼成功而已。不敢顾其传序之常。父子之情者。亦昭烈之心也。故非不知尧舜三王之所未有。伊尹周公之所不敢。亮之所必不为。而不能不以为言者。盖以明吾心之如此而已。岂不悲哉。诸葛亮七擒孟获
孔明之事。大抵未有不可晓者。袭刘璋取益州。孔明亦岂不知其不可。而以为不如此。则无以行吾之事。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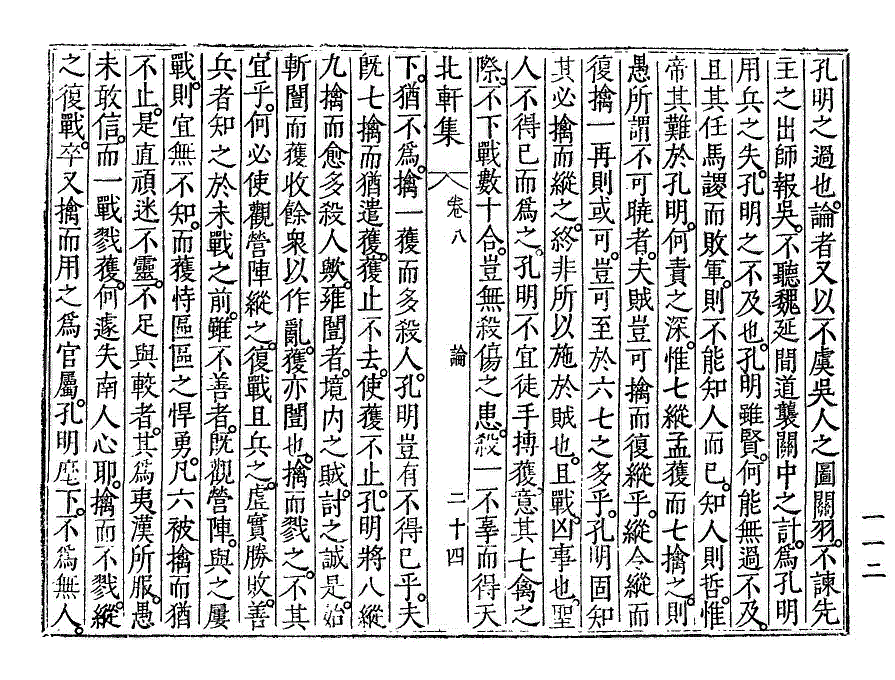 孔明之过也。论者又以不虞吴人之图关羽。不谏先主之出师报吴。不听魏延间道袭关中之计。为孔明用兵之失。孔明之不及也。孔明虽贤。何能无过不及。且其任马谡而败军。则不能知人而已。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于孔明。何责之深。惟七纵孟获而七擒之。则愚所谓不可晓者。夫贼岂可擒而复纵乎。纵令纵而复擒一再则或可。岂可至于六七之多乎。孔明固知其必擒而纵之。终非所以施于贼也。且战。凶事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孔明不宜徒手搏获。意其七禽之际。不下战数十合。岂无杀伤之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不为。擒一获而多杀人。孔明岂有不得已乎。夫既七擒而犹遣获。获止不去。使获不止。孔明将八纵九擒而愈多杀人欤。雍闿者。境内之贼。讨之诚是。始斩闿而获收馀众以作乱。获亦闿也。擒而戮之。不其宜乎。何必使观营阵纵之。复战且兵之。虚实胜败。善兵者知之于未战之前。虽不善者。既观营阵。与之屡战。则宜无不知。而获恃区区之悍勇。凡六被擒而犹不止。是直顽迷不灵。不足与较者。其为夷汉所服。愚未敢信。而一战戮获。何遽失南人心耶。擒而不戮。纵之复战。卒又擒而用之为官属。孔明麾下。不为无人。
孔明之过也。论者又以不虞吴人之图关羽。不谏先主之出师报吴。不听魏延间道袭关中之计。为孔明用兵之失。孔明之不及也。孔明虽贤。何能无过不及。且其任马谡而败军。则不能知人而已。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于孔明。何责之深。惟七纵孟获而七擒之。则愚所谓不可晓者。夫贼岂可擒而复纵乎。纵令纵而复擒一再则或可。岂可至于六七之多乎。孔明固知其必擒而纵之。终非所以施于贼也。且战。凶事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孔明不宜徒手搏获。意其七禽之际。不下战数十合。岂无杀伤之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不为。擒一获而多杀人。孔明岂有不得已乎。夫既七擒而犹遣获。获止不去。使获不止。孔明将八纵九擒而愈多杀人欤。雍闿者。境内之贼。讨之诚是。始斩闿而获收馀众以作乱。获亦闿也。擒而戮之。不其宜乎。何必使观营阵纵之。复战且兵之。虚实胜败。善兵者知之于未战之前。虽不善者。既观营阵。与之屡战。则宜无不知。而获恃区区之悍勇。凡六被擒而犹不止。是直顽迷不灵。不足与较者。其为夷汉所服。愚未敢信。而一战戮获。何遽失南人心耶。擒而不戮。纵之复战。卒又擒而用之为官属。孔明麾下。不为无人。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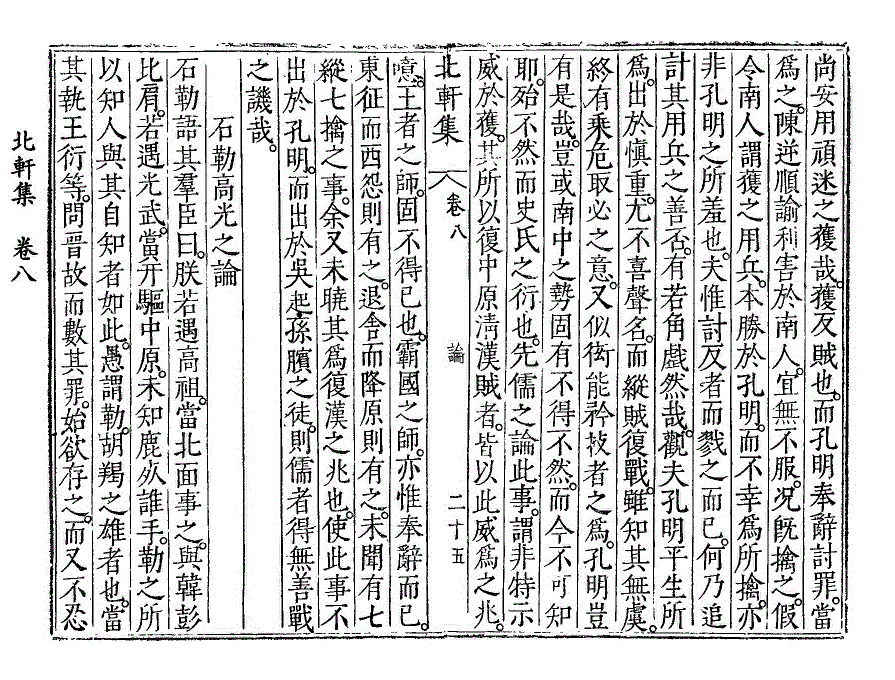 尚安用顽迷之获哉。获反贼也。而孔明奉辞讨罪。当为之。陈逆顺谕利害于南人。宜无不服。况既擒之。假令南人谓获之用兵。本胜于孔明。而不幸为所擒。亦非孔明之所羞也。夫惟讨反者而戮之而已。何乃追计其用兵之善否。有若角戏然哉。观夫孔明平生所为。出于慎重。尤不喜声名。而纵贼复战。虽知其无虞。终有乘危取必之意。又似衒能矜技者之为。孔明岂有是哉。岂或南中之势固有不得不然。而今不可知耶。殆不然而史氏之衍也。先儒之论此事。谓非特示威于获。其所以复中原清汉贼者。皆以此威为之兆。噫。王者之师。固不得已也。霸国之师。亦惟奉辞而已。东征而西怨则有之。退舍而降原则有之。未闻有七纵七擒之事。余又未晓其为复汉之兆也。使此事不出于孔明。而出于吴起,孙膑之徒。则儒者得无善战之讥哉。
尚安用顽迷之获哉。获反贼也。而孔明奉辞讨罪。当为之。陈逆顺谕利害于南人。宜无不服。况既擒之。假令南人谓获之用兵。本胜于孔明。而不幸为所擒。亦非孔明之所羞也。夫惟讨反者而戮之而已。何乃追计其用兵之善否。有若角戏然哉。观夫孔明平生所为。出于慎重。尤不喜声名。而纵贼复战。虽知其无虞。终有乘危取必之意。又似衒能矜技者之为。孔明岂有是哉。岂或南中之势固有不得不然。而今不可知耶。殆不然而史氏之衍也。先儒之论此事。谓非特示威于获。其所以复中原清汉贼者。皆以此威为之兆。噫。王者之师。固不得已也。霸国之师。亦惟奉辞而已。东征而西怨则有之。退舍而降原则有之。未闻有七纵七擒之事。余又未晓其为复汉之兆也。使此事不出于孔明。而出于吴起,孙膑之徒。则儒者得无善战之讥哉。石勒高光之论
石勒语其群臣曰。朕若遇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勒之所以知人与其自知者如此。愚谓勒。胡羯之雄者也。当其执王衍等。问晋故而数其罪。始欲存之。而又不忍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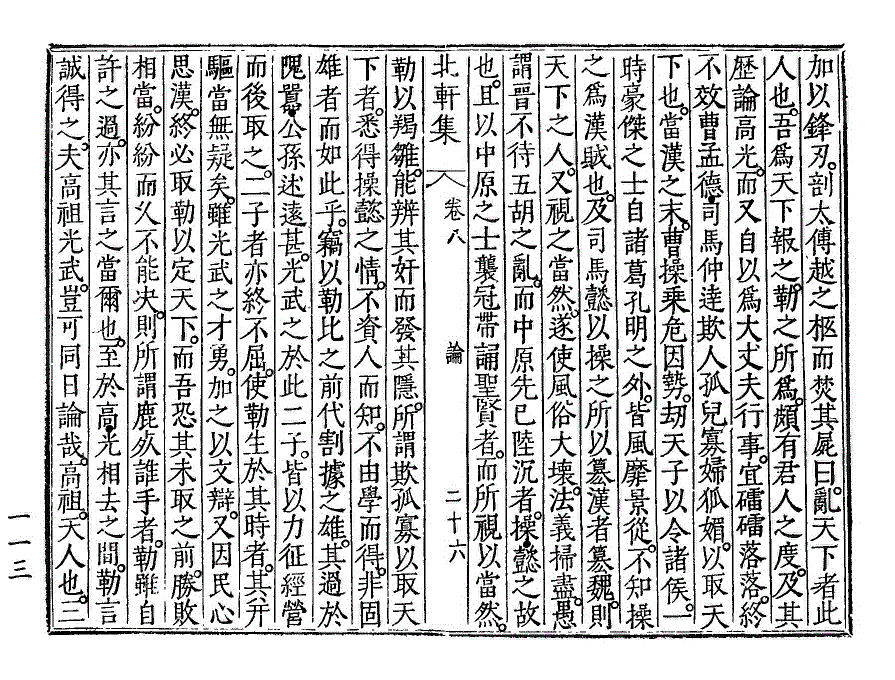 加以锋刃。剖太傅越之柩而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勒之所为。颇有君人之度。及其历论高光。而又自以为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当汉之末。曹操乘危因势。劫天子以令诸侯。一时豪杰之士自诸葛孔明之外。皆风靡景从。不知操之为汉贼也。及司马懿以操之所以篡汉者篡魏。则天下之人。又视之当然。遂使风俗大坏。法义扫尽。愚谓晋不待五胡之乱。而中原先已陆沉者。操,懿之故也。且以中原之士袭冠带诵圣贤者。而所视以当然。勒以羯雏。能辨其奸而发其隐。所谓欺孤寡以取天下者。悉得操懿之情。不资人而知。不由学而得。非固雄者而如此乎。窃以勒比之前代割据之雄。其过于隗嚣,公孙述远甚。光武之于此二子。皆以力征经营而后取之。二子者亦终不屈。使勒生于其时者。其并驱当无疑矣。虽光武之才勇。加之以文辩。又因民心思汉。终必取勒以定天下。而吾恐其未取之前。胜败相当。纷纷而久不能决。则所谓鹿死谁手者。勒虽自许之过。亦其言之当尔也。至于高,光相去之间。勒言诚得之。夫高祖光武。岂可同日论哉。高祖。天人也。三
加以锋刃。剖太傅越之柩而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勒之所为。颇有君人之度。及其历论高光。而又自以为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当汉之末。曹操乘危因势。劫天子以令诸侯。一时豪杰之士自诸葛孔明之外。皆风靡景从。不知操之为汉贼也。及司马懿以操之所以篡汉者篡魏。则天下之人。又视之当然。遂使风俗大坏。法义扫尽。愚谓晋不待五胡之乱。而中原先已陆沉者。操,懿之故也。且以中原之士袭冠带诵圣贤者。而所视以当然。勒以羯雏。能辨其奸而发其隐。所谓欺孤寡以取天下者。悉得操懿之情。不资人而知。不由学而得。非固雄者而如此乎。窃以勒比之前代割据之雄。其过于隗嚣,公孙述远甚。光武之于此二子。皆以力征经营而后取之。二子者亦终不屈。使勒生于其时者。其并驱当无疑矣。虽光武之才勇。加之以文辩。又因民心思汉。终必取勒以定天下。而吾恐其未取之前。胜败相当。纷纷而久不能决。则所谓鹿死谁手者。勒虽自许之过。亦其言之当尔也。至于高,光相去之间。勒言诚得之。夫高祖光武。岂可同日论哉。高祖。天人也。三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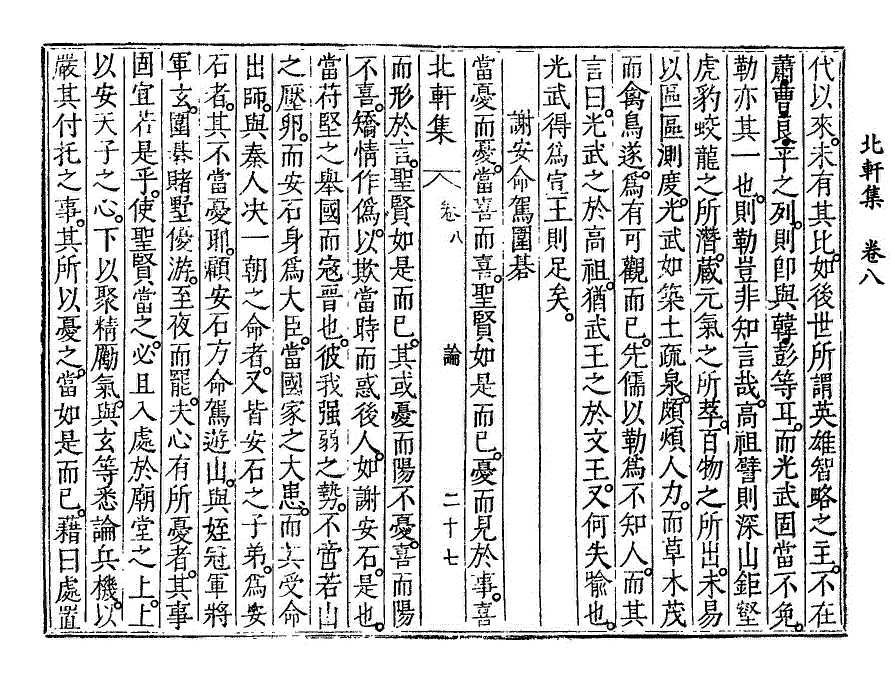 代以来。未有其比。如后世所谓英雄智略之主。不在萧,曹,良,平之列。则即与韩,彭等耳。而光武固当不免。勒亦其一也。则勒岂非知言哉。高祖譬则深山钜壑虎豹蛟龙之所潜。藏元气之所萃。百物之所出。未易以区区测度。光武如筑土疏泉。颇烦人力。而草木茂而禽鸟遂。为有可观而已。先儒以勒为不知人。而其言曰。光武之于高祖。犹武王之于文王。又何失喻也。光武得为宣王则足矣。
代以来。未有其比。如后世所谓英雄智略之主。不在萧,曹,良,平之列。则即与韩,彭等耳。而光武固当不免。勒亦其一也。则勒岂非知言哉。高祖譬则深山钜壑虎豹蛟龙之所潜。藏元气之所萃。百物之所出。未易以区区测度。光武如筑土疏泉。颇烦人力。而草木茂而禽鸟遂。为有可观而已。先儒以勒为不知人。而其言曰。光武之于高祖。犹武王之于文王。又何失喻也。光武得为宣王则足矣。谢安命驾围棋
当忧而忧。当喜而喜。圣贤如是而已。忧而见于事。喜而形于言。圣贤如是而已。其或忧而阳不忧。喜而阳不喜。矫情作伪。以欺当时而惑后人。如谢安石。是也。当苻坚之举国而寇晋也。彼我强弱之势。不啻若山之压卵。而安石身为大臣。当国家之大患。而其受命出师。与秦人决一朝之命者。又皆安石之子弟。为安石者。其不当忧耶。顾安石方命驾游山。与侄冠军将军玄。围棋赌墅优游。至夜而罢。夫心有所忧者。其事固宜若是乎。使圣贤当之。必且入处于庙堂之上。上以安天子之心。下以聚精励气。与玄等悉论兵机。以严其付托之事。其所以忧之。当如是而已。藉曰处置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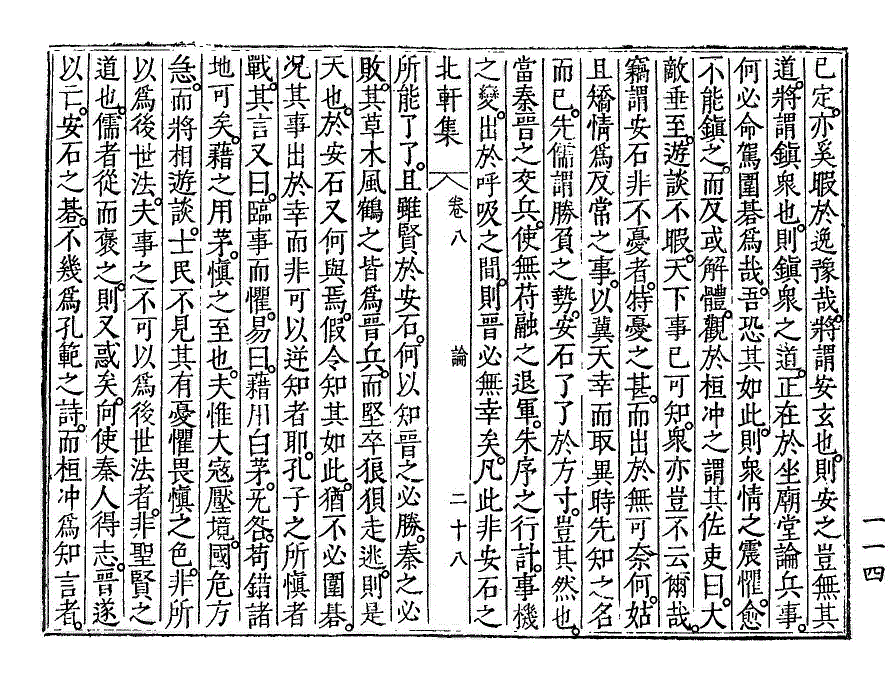 已定。亦奚暇于逸豫哉。将谓安玄也。则安之岂无其道。将谓镇众也。则镇众之道。正在于坐庙堂论兵事。何必命驾围棋为哉。吾恐其如此。则众情之震惧。愈不能镇之。而反或解体。观于桓冲之谓其佐吏曰。大敌垂至。游谈不暇。天下事已可知。众亦岂不云尔哉。窃谓安石非不忧者。特忧之甚。而出于无可奈何。姑且矫情为反常之事。以冀天幸而取异时先知之名而已。先儒谓胜负之势。安石了了于方寸。岂其然也。当秦晋之交兵。使无苻融之退军。朱序之行计。事机之变。出于呼吸之间。则晋必无幸矣。凡此非安石之所能了了。且虽贤于安石。何以知晋之必胜。秦之必败。其草木风鹤之皆为晋兵。而坚卒狼狈走逃。则是天也。于安石又何与焉。假令知其如此。犹不必围棋。况其事出于幸而非可以逆知者耶。孔子之所慎者战。其言又曰。临事而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错诸地可矣。藉之用茅。慎之至也。夫惟大寇压境。国危方急。而将相游谈。士民不见其有忧惧畏慎之色。非所以为后世法。夫事之不可以为后世法者。非圣贤之道也。儒者从而褒之。则又惑矣。向使秦人得志。晋遂以亡。安石之棋。不几为孔范之诗。而桓冲为知言者。
已定。亦奚暇于逸豫哉。将谓安玄也。则安之岂无其道。将谓镇众也。则镇众之道。正在于坐庙堂论兵事。何必命驾围棋为哉。吾恐其如此。则众情之震惧。愈不能镇之。而反或解体。观于桓冲之谓其佐吏曰。大敌垂至。游谈不暇。天下事已可知。众亦岂不云尔哉。窃谓安石非不忧者。特忧之甚。而出于无可奈何。姑且矫情为反常之事。以冀天幸而取异时先知之名而已。先儒谓胜负之势。安石了了于方寸。岂其然也。当秦晋之交兵。使无苻融之退军。朱序之行计。事机之变。出于呼吸之间。则晋必无幸矣。凡此非安石之所能了了。且虽贤于安石。何以知晋之必胜。秦之必败。其草木风鹤之皆为晋兵。而坚卒狼狈走逃。则是天也。于安石又何与焉。假令知其如此。犹不必围棋。况其事出于幸而非可以逆知者耶。孔子之所慎者战。其言又曰。临事而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错诸地可矣。藉之用茅。慎之至也。夫惟大寇压境。国危方急。而将相游谈。士民不见其有忧惧畏慎之色。非所以为后世法。夫事之不可以为后世法者。非圣贤之道也。儒者从而褒之。则又惑矣。向使秦人得志。晋遂以亡。安石之棋。不几为孔范之诗。而桓冲为知言者。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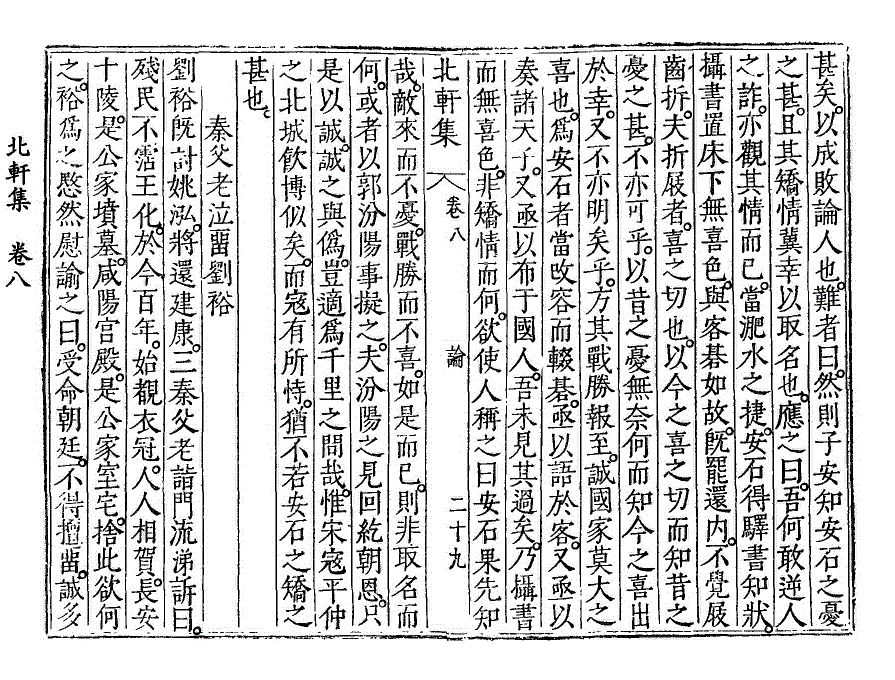 甚矣。以成败论人也。难者曰。然则子安知安石之忧之甚。且其矫情冀幸以取名也。应之曰。吾何敢逆人之诈。亦观其情而已。当淝水之捷。安石得驿书知状。摄书置床下无喜色。与客棋如故。既罢还内。不觉屐齿拆。夫折屐者。喜之切也。以今之喜之切而知昔之忧之甚。不亦可乎。以昔之忧无奈何而知今之喜出于幸。又不亦明矣乎。方其战胜报至。诚国家莫大之喜也。为安石者当改容而辍棋。亟以语于客。又亟以奏诸天子。又亟以布于国人。吾未见其过矣。乃摄书而无喜色。非矫情而何。欲使人称之曰安石果先知哉。敌来而不忧。战胜而不喜。如是而已。则非取名而何。或者以郭汾阳事拟之。夫汾阳之见回纥朝恩。只是以诚。诚之与伪。岂适为千里之间哉。惟宋寇平仲之北城饮博似矣。而寇有所恃。犹不若安石之矫之甚也。
甚矣。以成败论人也。难者曰。然则子安知安石之忧之甚。且其矫情冀幸以取名也。应之曰。吾何敢逆人之诈。亦观其情而已。当淝水之捷。安石得驿书知状。摄书置床下无喜色。与客棋如故。既罢还内。不觉屐齿拆。夫折屐者。喜之切也。以今之喜之切而知昔之忧之甚。不亦可乎。以昔之忧无奈何而知今之喜出于幸。又不亦明矣乎。方其战胜报至。诚国家莫大之喜也。为安石者当改容而辍棋。亟以语于客。又亟以奏诸天子。又亟以布于国人。吾未见其过矣。乃摄书而无喜色。非矫情而何。欲使人称之曰安石果先知哉。敌来而不忧。战胜而不喜。如是而已。则非取名而何。或者以郭汾阳事拟之。夫汾阳之见回纥朝恩。只是以诚。诚之与伪。岂适为千里之间哉。惟宋寇平仲之北城饮博似矣。而寇有所恃。犹不若安石之矫之甚也。秦父老泣留刘裕
刘裕既讨姚泓。将还建康。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裕为之悯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诚多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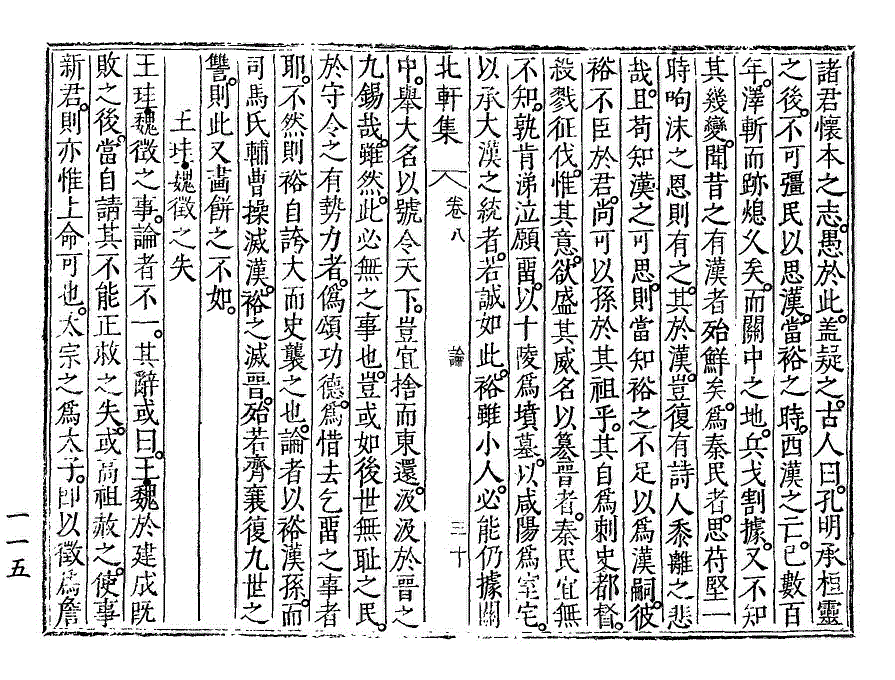 诸君怀本之志。愚于此。盖疑之。古人曰。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彊民以思汉。当裕之时。西汉之亡。已数百年。泽斩而迹熄久矣。而关中之地。兵戈割据。又不知其几变。闻昔之有汉者殆鲜矣。为秦民者。思苻坚一时呴沫之恩则有之。其于汉。岂复有诗人黍离之悲哉。且苟知汉之可思。则当知裕之不足以为汉嗣。彼裕不臣于君。尚可以孙于其祖乎。其自为刺史都督。杀戮征伐。惟其意。欲盛其威名以篡晋者。秦民宜无不知。孰肯涕泣愿留。以十陵为坟墓。以咸阳为室宅。以承大汉之统者。若诚如此。裕虽小人。必能仍据关中。举大名以号令天下。岂宜舍而东还。汲汲于晋之九锡哉。虽然。此必无之事也。岂或如后世无耻之民。于守令之有势力者。伪颂功德。为惜去乞留之事者耶。不然则裕自誇大而史袭之也。论者以裕汉孙。而司马氏辅曹操灭汉。裕之灭晋。殆若齐襄复九世之雠。则此又画饼之不如。
诸君怀本之志。愚于此。盖疑之。古人曰。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彊民以思汉。当裕之时。西汉之亡。已数百年。泽斩而迹熄久矣。而关中之地。兵戈割据。又不知其几变。闻昔之有汉者殆鲜矣。为秦民者。思苻坚一时呴沫之恩则有之。其于汉。岂复有诗人黍离之悲哉。且苟知汉之可思。则当知裕之不足以为汉嗣。彼裕不臣于君。尚可以孙于其祖乎。其自为刺史都督。杀戮征伐。惟其意。欲盛其威名以篡晋者。秦民宜无不知。孰肯涕泣愿留。以十陵为坟墓。以咸阳为室宅。以承大汉之统者。若诚如此。裕虽小人。必能仍据关中。举大名以号令天下。岂宜舍而东还。汲汲于晋之九锡哉。虽然。此必无之事也。岂或如后世无耻之民。于守令之有势力者。伪颂功德。为惜去乞留之事者耶。不然则裕自誇大而史袭之也。论者以裕汉孙。而司马氏辅曹操灭汉。裕之灭晋。殆若齐襄复九世之雠。则此又画饼之不如。王圭,魏徵之失
王圭,魏徵之事。论者不一。其辞或曰。王,魏于建成既败之后。当自请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则亦惟上命可也。太宗之为太子。即以徵为詹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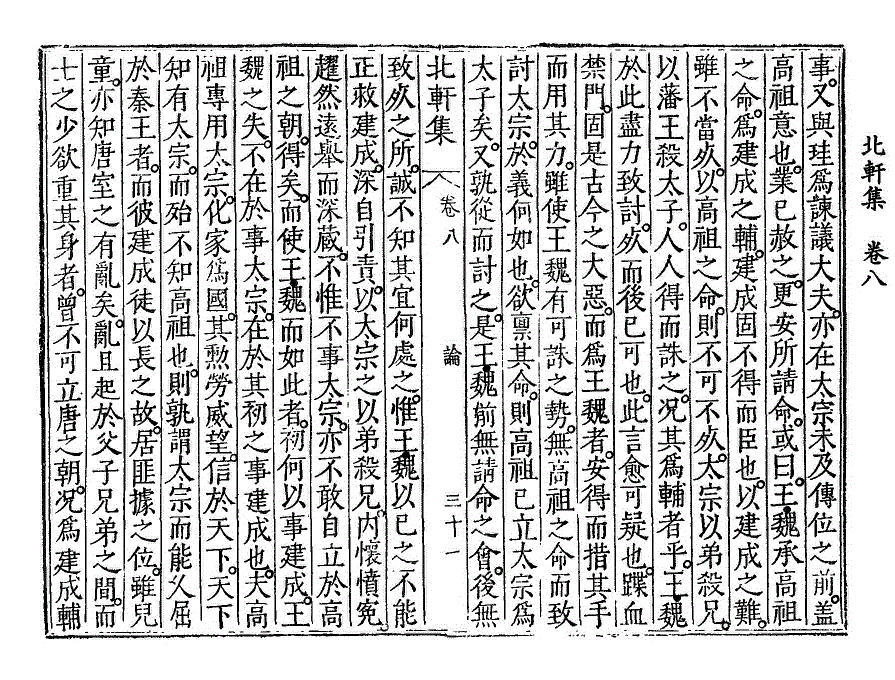 事。又与圭为谏议大夫。亦在太宗未及传位之前。盖高祖意也。业已赦之。更安所请命。或曰。王,魏承高祖之命。为建成之辅。建成固不得而臣也。以建成之难。虽不当死。以高祖之命。则不可不死。太宗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况其为辅者乎。王,魏于此尽力致讨。死而后已可也。此言愈可疑也。蹀血禁门。固是古今之大恶。而为王魏者。安得而措其手而用其力。虽使王魏有可诛之势。无高祖之命而致讨太宗。于义何如也。欲禀其命。则高祖已立太宗为太子矣。又孰从而讨之。是王,魏前无请命之会。后无致死之所。诚不知其宜何处之。惟王,魏以己之不能正救建成。深自引责。以太宗之以弟杀兄。内怀愤冤。趯然远举而深藏。不惟不事太宗。亦不敢自立于高祖之朝。得矣。而使王,魏而如此者。初何以事建成。王魏之失。不在于事太宗。在于其初之事建成也。夫高祖专用太宗。化家为国。其勋劳威望。信于天下。天下知有太宗。而殆不知高祖也。则孰谓太宗而能久屈于秦王者。而彼建成徒以长之故。居匪据之位。虽儿童。亦知唐室之有乱矣。乱且起于父子兄弟之间。而士之少欲重其身者。曾不可立唐之朝。况为建成辅
事。又与圭为谏议大夫。亦在太宗未及传位之前。盖高祖意也。业已赦之。更安所请命。或曰。王,魏承高祖之命。为建成之辅。建成固不得而臣也。以建成之难。虽不当死。以高祖之命。则不可不死。太宗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况其为辅者乎。王,魏于此尽力致讨。死而后已可也。此言愈可疑也。蹀血禁门。固是古今之大恶。而为王魏者。安得而措其手而用其力。虽使王魏有可诛之势。无高祖之命而致讨太宗。于义何如也。欲禀其命。则高祖已立太宗为太子矣。又孰从而讨之。是王,魏前无请命之会。后无致死之所。诚不知其宜何处之。惟王,魏以己之不能正救建成。深自引责。以太宗之以弟杀兄。内怀愤冤。趯然远举而深藏。不惟不事太宗。亦不敢自立于高祖之朝。得矣。而使王,魏而如此者。初何以事建成。王魏之失。不在于事太宗。在于其初之事建成也。夫高祖专用太宗。化家为国。其勋劳威望。信于天下。天下知有太宗。而殆不知高祖也。则孰谓太宗而能久屈于秦王者。而彼建成徒以长之故。居匪据之位。虽儿童。亦知唐室之有乱矣。乱且起于父子兄弟之间。而士之少欲重其身者。曾不可立唐之朝。况为建成辅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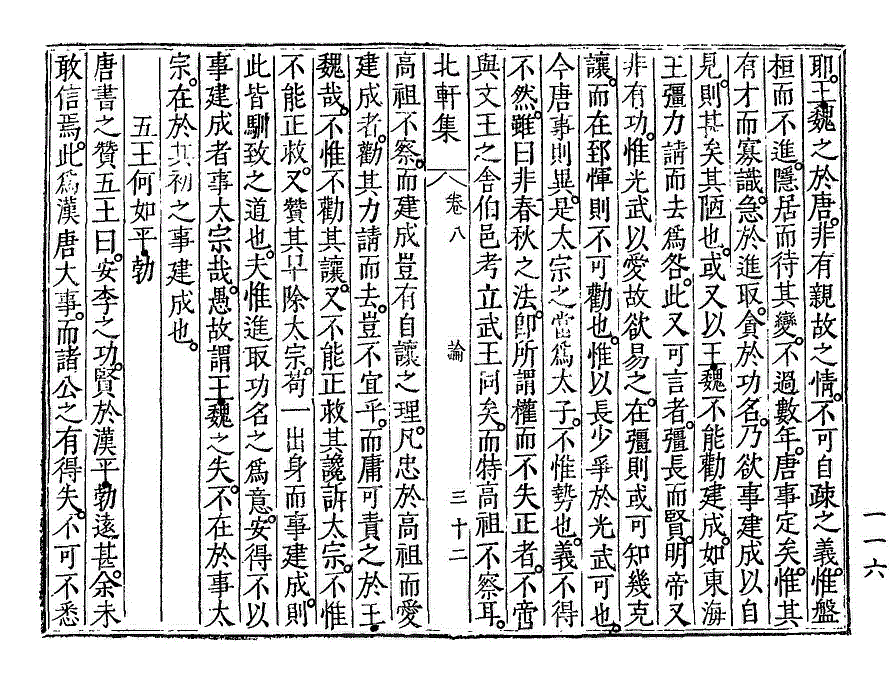 耶。王,魏之于唐。非有亲故之情。不可自疏之义。惟盘桓而不进。隐居而待其变。不过数年。唐事定矣。惟其有才而寡识。急于进取。贪于功名。乃欲事建成以自见。则甚矣其陋也。或又以王,魏不能劝建成。如东海王彊力请而去为咎。此又可言者。彊长而贤。明帝又非有功。惟光武以爱故欲易之。在彊则或可知几克让。而在郅恽则不可劝也。惟以长少争于光武可也。今唐事则异。是太宗之当为太子。不惟势也。义不得不然。虽曰非春秋之法。即所谓权而不失正者。不啻与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同矣。而特高祖不察耳。高祖不察。而建成岂有自让之理。凡忠于高祖而爱建成者。劝其力请而去。岂不宜乎。而庸可责之于王,魏哉。不惟不劝其让。又不能正救其谗诉太宗。不惟不能正救。又赞其早除太宗。苟一出身而事建成。则此皆驯致之道也。夫惟进取功名之为意。安得不以事建成者事太宗哉。愚故谓王,魏之失。不在于事太宗。在于其初之事建成也。
耶。王,魏之于唐。非有亲故之情。不可自疏之义。惟盘桓而不进。隐居而待其变。不过数年。唐事定矣。惟其有才而寡识。急于进取。贪于功名。乃欲事建成以自见。则甚矣其陋也。或又以王,魏不能劝建成。如东海王彊力请而去为咎。此又可言者。彊长而贤。明帝又非有功。惟光武以爱故欲易之。在彊则或可知几克让。而在郅恽则不可劝也。惟以长少争于光武可也。今唐事则异。是太宗之当为太子。不惟势也。义不得不然。虽曰非春秋之法。即所谓权而不失正者。不啻与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同矣。而特高祖不察耳。高祖不察。而建成岂有自让之理。凡忠于高祖而爱建成者。劝其力请而去。岂不宜乎。而庸可责之于王,魏哉。不惟不劝其让。又不能正救其谗诉太宗。不惟不能正救。又赞其早除太宗。苟一出身而事建成。则此皆驯致之道也。夫惟进取功名之为意。安得不以事建成者事太宗哉。愚故谓王,魏之失。不在于事太宗。在于其初之事建成也。五王何如平,勃
唐书之赞五王曰。安李之功。贤于汉平,勃远甚。余未敢信焉。此为汉唐大事。而诸公之有得失。不可不悉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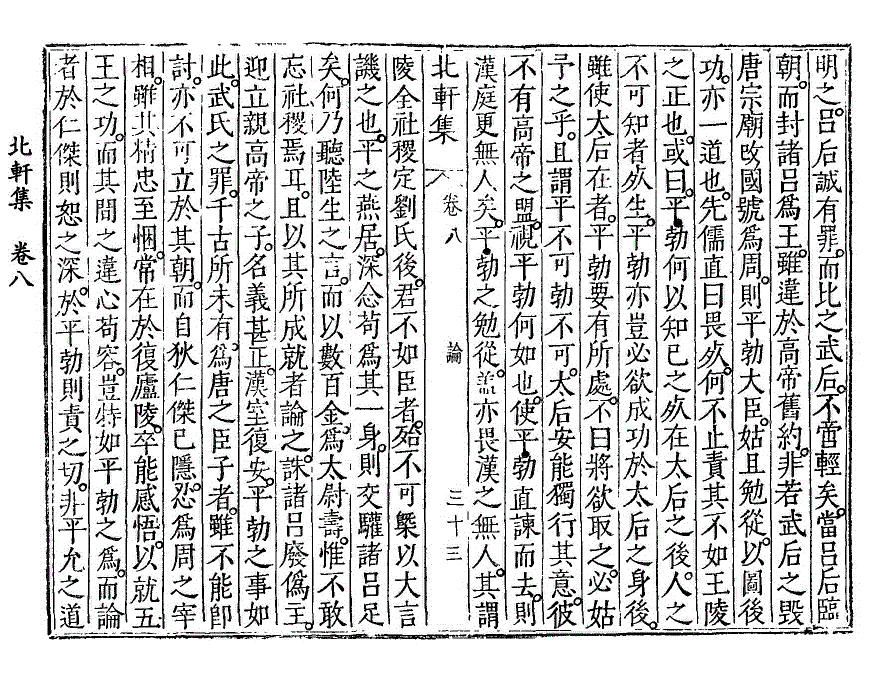 明之。吕后诚有罪。而比之武后。不啻轻矣。当吕后临朝。而封诸吕为王。虽违于高帝旧约。非若武后之毁唐宗庙改国号为周。则平,勃大臣。姑且勉从。以图后功。亦一道也。先儒直曰畏死。何不止责其不如王陵之正也。或曰。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后。人之不可知者死生。平,勃亦岂必欲成功于太后之身后。虽使太后在者。平,勃要有所处。不曰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乎。且谓平不可勃不可。太后安能独行其意。彼不有高帝之盟。视平,勃何如也。使平,勃直谏而去。则汉庭更无人矣。平,勃之勉从。盖亦畏汉之无人。其谓陵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不如臣者。殆不可槩以大言讥之也。平之燕居。深念苟为其一身。则交驩诸吕足矣。何乃听陆生之言。而以数百金。为太尉寿。惟不敢忘社稷焉耳。且以其所成就者论之。诛诸吕废伪主。迎立亲高帝之子。名义甚正。汉室复安。平,勃之事如此。武氏之罪。千古所未有。为唐之臣子者。虽不能即讨。亦不可立于其朝。而自狄仁杰已隐。忍为周之宰相。虽其精忠至悃。常在于复庐陵。卒能感悟。以就五王之功。而其间之违心苟容。岂特如平,勃之为。而论者于仁杰则恕之深。于平,勃则责之切。非平允之道
明之。吕后诚有罪。而比之武后。不啻轻矣。当吕后临朝。而封诸吕为王。虽违于高帝旧约。非若武后之毁唐宗庙改国号为周。则平,勃大臣。姑且勉从。以图后功。亦一道也。先儒直曰畏死。何不止责其不如王陵之正也。或曰。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后。人之不可知者死生。平,勃亦岂必欲成功于太后之身后。虽使太后在者。平,勃要有所处。不曰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乎。且谓平不可勃不可。太后安能独行其意。彼不有高帝之盟。视平,勃何如也。使平,勃直谏而去。则汉庭更无人矣。平,勃之勉从。盖亦畏汉之无人。其谓陵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不如臣者。殆不可槩以大言讥之也。平之燕居。深念苟为其一身。则交驩诸吕足矣。何乃听陆生之言。而以数百金。为太尉寿。惟不敢忘社稷焉耳。且以其所成就者论之。诛诸吕废伪主。迎立亲高帝之子。名义甚正。汉室复安。平,勃之事如此。武氏之罪。千古所未有。为唐之臣子者。虽不能即讨。亦不可立于其朝。而自狄仁杰已隐。忍为周之宰相。虽其精忠至悃。常在于复庐陵。卒能感悟。以就五王之功。而其间之违心苟容。岂特如平,勃之为。而论者于仁杰则恕之深。于平,勃则责之切。非平允之道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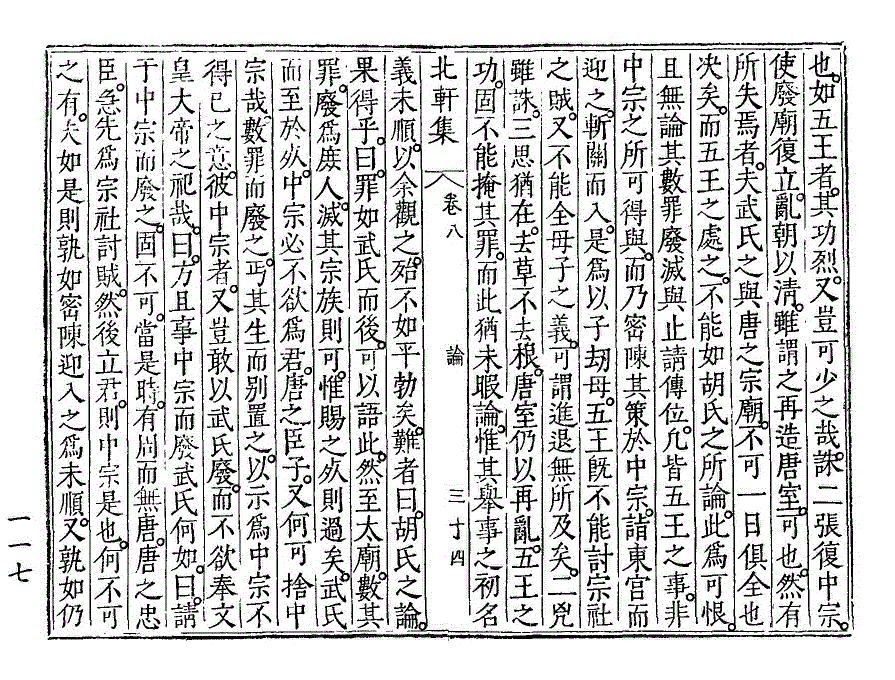 也。如五王者。其功烈。又岂可少之哉。诛二张复中宗。使废庙复立。乱朝以清。虽谓之再造唐室。可也。然有所失焉者。夫武氏之与唐之宗庙。不可一日俱全也决矣。而五王之处之。不能如胡氏之所论。此为可恨。且无论其数罪废灭与止请传位。凡皆五王之事。非中宗之所可得与。而乃密陈其策于中宗。诣东宫而迎之。斩关而入。是为以子劫母。五王既不能讨宗社之贼。又不能全母子之义。可谓进退无所及矣。二凶虽诛。三思犹在。去草不去根。唐室仍以再乱。五王之功。固不能掩其罪。而此犹未暇论。惟其举事之初名义未顺。以余观之。殆不如平勃矣。难者曰。胡氏之论。果得乎。曰。罪如武氏而后。可以语此。然至太庙。数其罪。废为庶人。灭其宗族则可。惟赐之死则过矣。武氏而至于死。中宗必不欲为君。唐之臣子。又何可舍中宗哉。数罪而废之。丐其生而别置之。以示为中宗不得已之意。彼中宗者。又岂敢以武氏废。而不欲奉文皇大帝之祀哉。曰。方且事中宗而废武氏何如。曰。请于中宗而废之。固不可。当是时。有周而无唐。唐之忠臣。急先为宗社讨贼。然后立君。则中宗是也。何不可之有。夫如是则孰如密陈迎入之为未顺。又孰如仍
也。如五王者。其功烈。又岂可少之哉。诛二张复中宗。使废庙复立。乱朝以清。虽谓之再造唐室。可也。然有所失焉者。夫武氏之与唐之宗庙。不可一日俱全也决矣。而五王之处之。不能如胡氏之所论。此为可恨。且无论其数罪废灭与止请传位。凡皆五王之事。非中宗之所可得与。而乃密陈其策于中宗。诣东宫而迎之。斩关而入。是为以子劫母。五王既不能讨宗社之贼。又不能全母子之义。可谓进退无所及矣。二凶虽诛。三思犹在。去草不去根。唐室仍以再乱。五王之功。固不能掩其罪。而此犹未暇论。惟其举事之初名义未顺。以余观之。殆不如平勃矣。难者曰。胡氏之论。果得乎。曰。罪如武氏而后。可以语此。然至太庙。数其罪。废为庶人。灭其宗族则可。惟赐之死则过矣。武氏而至于死。中宗必不欲为君。唐之臣子。又何可舍中宗哉。数罪而废之。丐其生而别置之。以示为中宗不得已之意。彼中宗者。又岂敢以武氏废。而不欲奉文皇大帝之祀哉。曰。方且事中宗而废武氏何如。曰。请于中宗而废之。固不可。当是时。有周而无唐。唐之忠臣。急先为宗社讨贼。然后立君。则中宗是也。何不可之有。夫如是则孰如密陈迎入之为未顺。又孰如仍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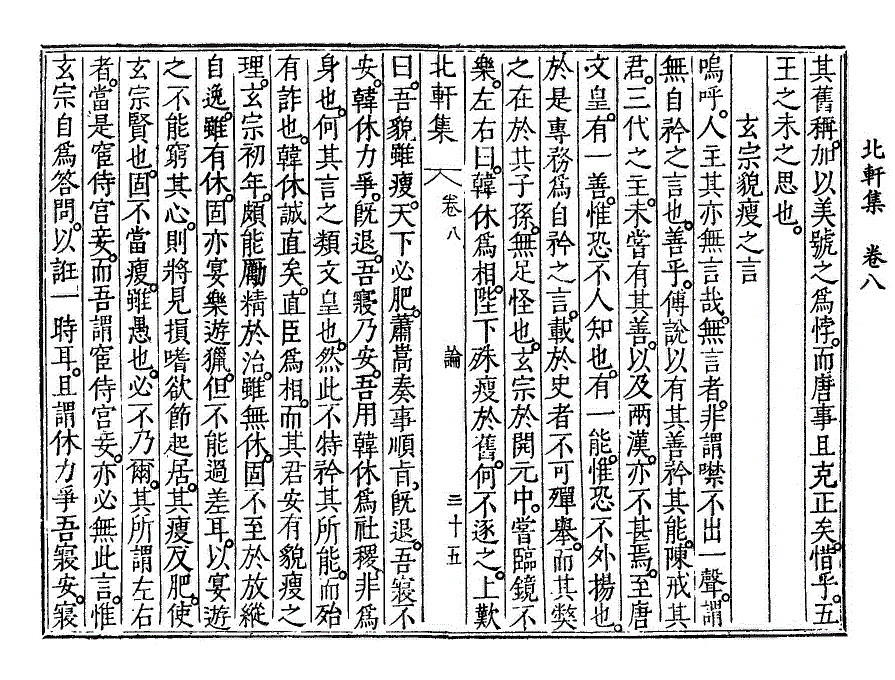 其旧称。加以美号之为悖。而唐事且克正矣。惜乎。五王之未之思也。
其旧称。加以美号之为悖。而唐事且克正矣。惜乎。五王之未之思也。玄宗貌瘦之言
呜呼。人主其亦无言哉。无言者。非谓噤不出一声。谓无自矜之言也。善乎。傅说以有其善矜其能。陈戒其君。三代之主。未尝有其善。以及两汉。亦不甚焉。至唐文皇。有一善。惟恐不人知也。有一能。惟恐不外扬也。于是专务为自矜之言。载于史者不可殚举。而其弊之在于其子孙。无足怪也。玄宗于开元中。尝临镜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顺旨。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非为身也。何其言之类文皇也。然此不特矜其所能。而殆有诈也。韩休诚直矣。直臣为相。而其君安有貌瘦之理。玄宗初年。颇能励精于治。虽无休。固不至于放纵自逸。虽有休。固亦宴乐游猎。但不能过差耳。以宴游之不能穷其心。则将见损嗜欲节起居。其瘦反肥。使玄宗贤也。固不当瘦。虽愚也。必不乃尔。其所谓左右者。当是宦侍宫妾。而吾谓宦侍宫妾。亦必无此言。惟玄宗自为答问。以诳一时耳。且谓休力争吾寝安。寝
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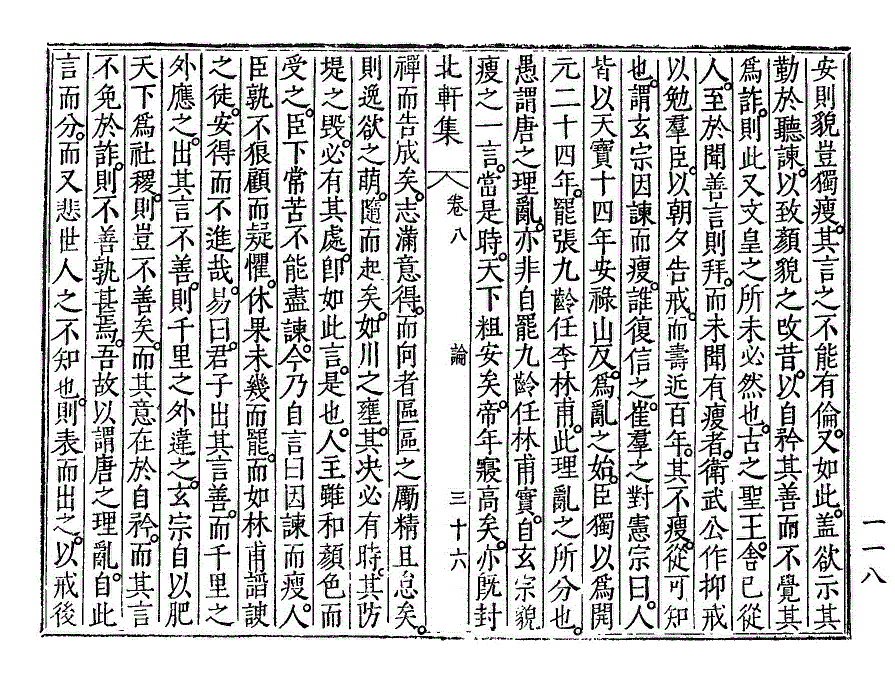 安则貌岂独瘦。其言之不能有伦。又如此。盖欲示其勤于听谏。以致颜貌之改昔。以自矜其善而不觉其为诈。则此又文皇之所未必然也。古之圣王。舍己从人。至于闻善言则拜。而未闻有瘦者。卫武公作抑戒以勉群臣。以朝夕告戒。而寿近百年。其不瘦。从可知也。谓玄宗因谏而瘦。谁复信之。崔群之对宪宗曰。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愚谓唐之理乱。亦非自罢九龄任林甫实。自玄宗貌瘦之一言。当是时。天下粗安矣。帝年寝高矣。亦既封禅而告成矣。志满意得。而向者区区之励精且怠矣。则逸欲之萌。随而起矣。如川之壅。其决必有时。其防堤之毁。必有其处。即如此言。是也。人主虽和颜色而受之。臣下常苦不能尽谏。今乃自言曰因谏而瘦。人臣孰不狼顾而疑惧。休果未几而罢。而如林甫谄谀之徒。安得而不进哉。易曰。君子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玄宗自以肥天下为社稷。则岂不善矣。而其意在于自矜。而其言不免于诈。则不善孰甚焉。吾故以谓唐之理乱。自此言而分。而又悲世人之不知也。则表而出之。以戒后
安则貌岂独瘦。其言之不能有伦。又如此。盖欲示其勤于听谏。以致颜貌之改昔。以自矜其善而不觉其为诈。则此又文皇之所未必然也。古之圣王。舍己从人。至于闻善言则拜。而未闻有瘦者。卫武公作抑戒以勉群臣。以朝夕告戒。而寿近百年。其不瘦。从可知也。谓玄宗因谏而瘦。谁复信之。崔群之对宪宗曰。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愚谓唐之理乱。亦非自罢九龄任林甫实。自玄宗貌瘦之一言。当是时。天下粗安矣。帝年寝高矣。亦既封禅而告成矣。志满意得。而向者区区之励精且怠矣。则逸欲之萌。随而起矣。如川之壅。其决必有时。其防堤之毁。必有其处。即如此言。是也。人主虽和颜色而受之。臣下常苦不能尽谏。今乃自言曰因谏而瘦。人臣孰不狼顾而疑惧。休果未几而罢。而如林甫谄谀之徒。安得而不进哉。易曰。君子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玄宗自以肥天下为社稷。则岂不善矣。而其意在于自矜。而其言不免于诈。则不善孰甚焉。吾故以谓唐之理乱。自此言而分。而又悲世人之不知也。则表而出之。以戒后北轩居士集卷之八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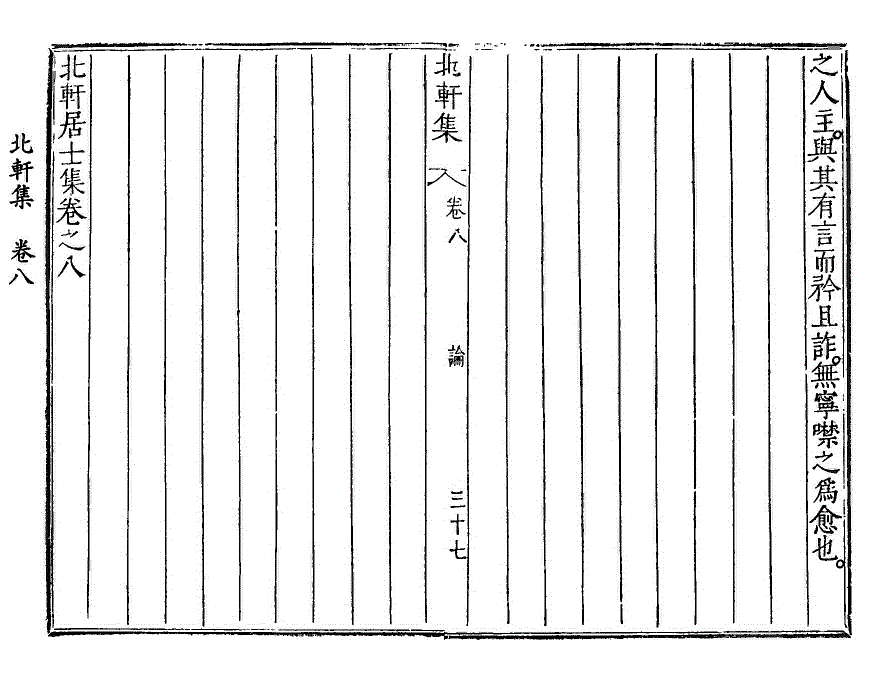 之人主。与其有言而矜且诈。无宁噤之为愈也。
之人主。与其有言而矜且诈。无宁噤之为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