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x 页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读书散录
读书散录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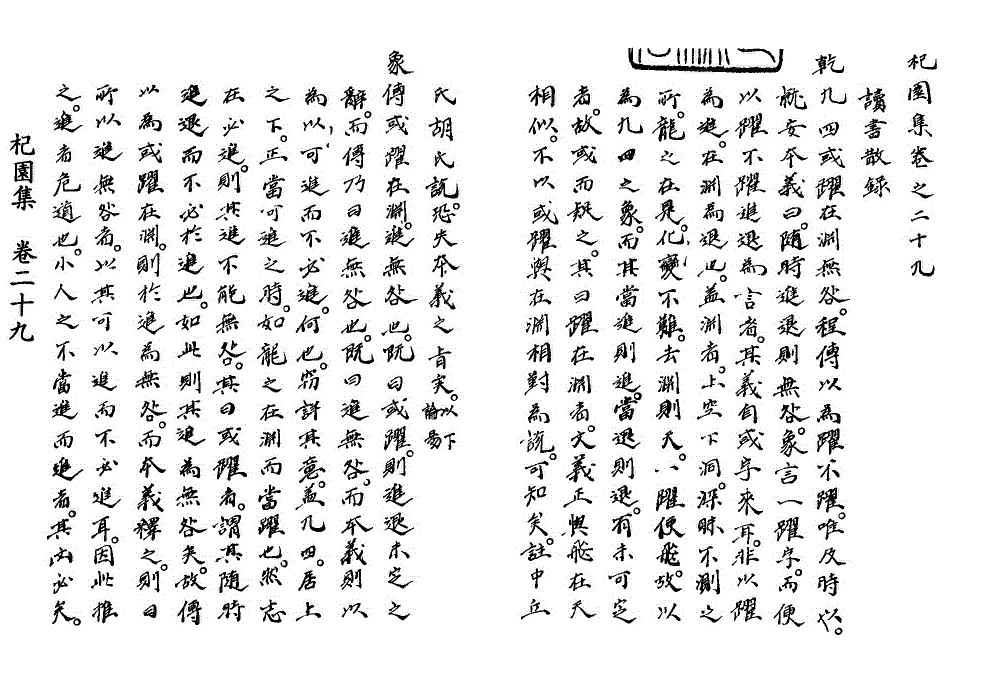 [易]
[易]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程传以为跃不跃。唯及时以。就安本义曰。随时进退则无咎。象言一跃字。而便以跃不跃进退为言者。其义自或字来耳。非以跃为进。在渊为退也。盖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变化不难。去渊则天。一跃便飞。故以为九四之象。而其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有未可定者。故或而疑之。其曰跃在渊者。文义正与飞在天相似。不以或跃与在渊相对为说。可知矣。注中丘氏胡氏说。恐失本义之旨矣。(以下论易)
象传或跃在渊。进无咎也。既曰或跃。则进退未定之辞。而传乃曰进无咎也。既曰进无咎。而本义则以为可以进而不必进。何也。窃详其意。盖九四。居上之下。正当可进之时。如龙之在渊而当跃也。然志在必进。则其进不能无咎。其曰或跃者。谓其随时进退而不必于进也。如此则其进为无咎矣。故传以为或跃在渊。则于进为无咎。而本义释之。则曰所以进无咎者。以其可以进而不必进耳。因此推之。进者危道也。小人之不当进而进者。其凶必矣。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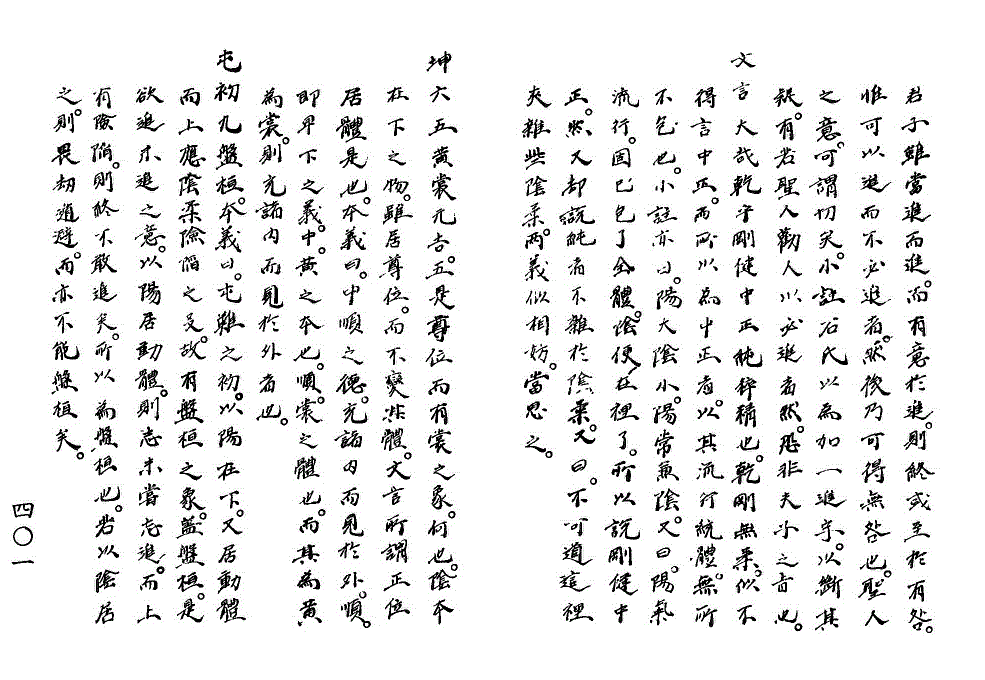 君子虽当进而进。而有意于进。则终或至于有咎。惟可以进而不必进者。然后乃可得无咎也。圣人之意。可谓切矣。小注石氏以为加一进字。以断其疑。有若圣人劝人以必进者然。恐非夫子之旨也。
君子虽当进而进。而有意于进。则终或至于有咎。惟可以进而不必进者。然后乃可得无咎也。圣人之意。可谓切矣。小注石氏以为加一进字。以断其疑。有若圣人劝人以必进者然。恐非夫子之旨也。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刚无柔。似不得言中正。而所以为中正者。以其流行统体。无所不包也。小注亦曰。阳大阴小。阳常兼阴。又曰。阳气流行。固已包了全体。阴便在里了。所以说刚健中正。然又却说纯者不杂于阴柔。又曰。不可道这里夹杂些阴柔。两义似相妨。当思之。
坤六五黄裳元吉。五是尊位而有裳之象。何也。阴本在下之物。虽居尊位。而不变其体。文言所谓正位居体是也。本义曰。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顺。即卑下之义。中。黄之本也。顺。裳之体也。而其为黄为裳。则充诸内而见于外者也。
屯初九盘桓。本义曰。屯难之初。以阳在下。又居动体而上应阴柔险陷之爻。故有盘桓之象。盖盘桓。是欲进未进之意。以阳居动体。则志未尝忘进。而上有险陷。则终不敢进矣。所以为盘桓也。若以阴居之。则畏劫遁避。而亦不能盘桓矣。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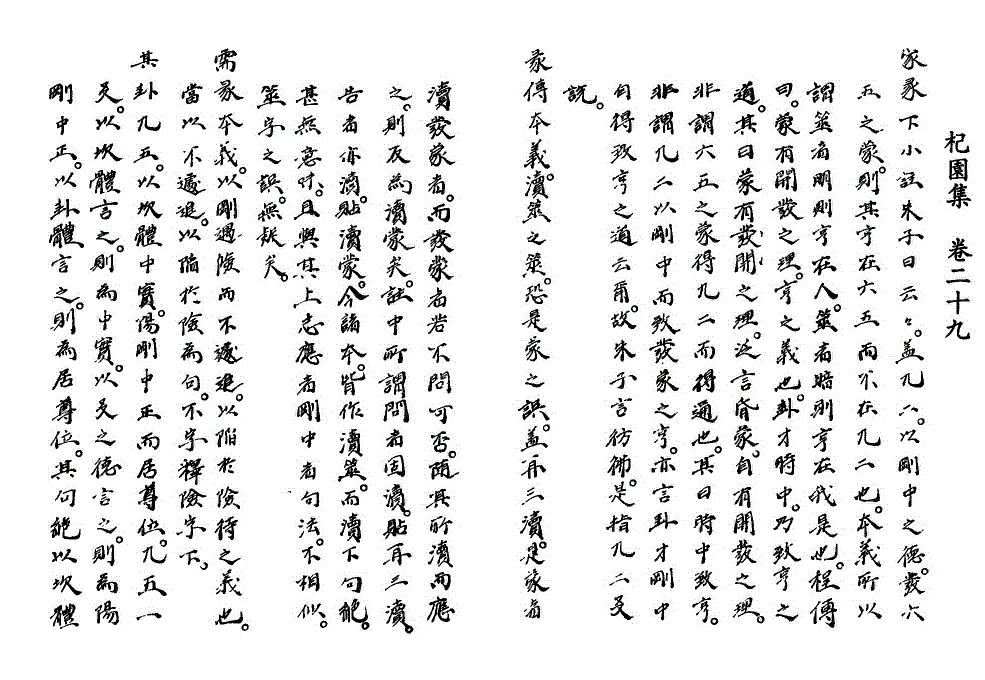 蒙彖下小注朱子曰云云。盖九二。以刚中之德。发六五之蒙。则其亨在六五而不在九二也。本义所以谓筮者明则亨在人。筮者暗则亨在我是也。程传曰。蒙有开发之理。亨之义也。卦才时中。乃致亨之道。其曰蒙有开发之理。泛言昏蒙。自有开发之理。非谓六五之蒙得九二而得通也。其曰时中致亨。非谓九二以刚中而致发蒙之亨。亦言卦才刚中自得致亨之道云尔。故朱子言彷佛。是指九二爻说。
蒙彖下小注朱子曰云云。盖九二。以刚中之德。发六五之蒙。则其亨在六五而不在九二也。本义所以谓筮者明则亨在人。筮者暗则亨在我是也。程传曰。蒙有开发之理。亨之义也。卦才时中。乃致亨之道。其曰蒙有开发之理。泛言昏蒙。自有开发之理。非谓六五之蒙得九二而得通也。其曰时中致亨。非谓九二以刚中而致发蒙之亨。亦言卦才刚中自得致亨之道云尔。故朱子言彷佛。是指九二爻说。彖传本义。渎筮之筮。恐是蒙之误。盖再三渎。是蒙者渎发蒙者。而发蒙者若不问可否。随其所渎而应之。则反为渎蒙矣。注中所谓问者固渎。贴再三渎。告者亦渎。贴渎蒙。今诸本。皆作渎筮。而渎下句绝。甚无意味。且与其上志应者刚中者句法。不相似。筮字之误。无疑矣。
需彖本义。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当以不遽进。以陷于险为句。不字释险字下。
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九五一爻。以坎体言之。则为中实。以爻之德言之。则为阳刚中正。以卦体言之。则为居尊位。其句绝以坎体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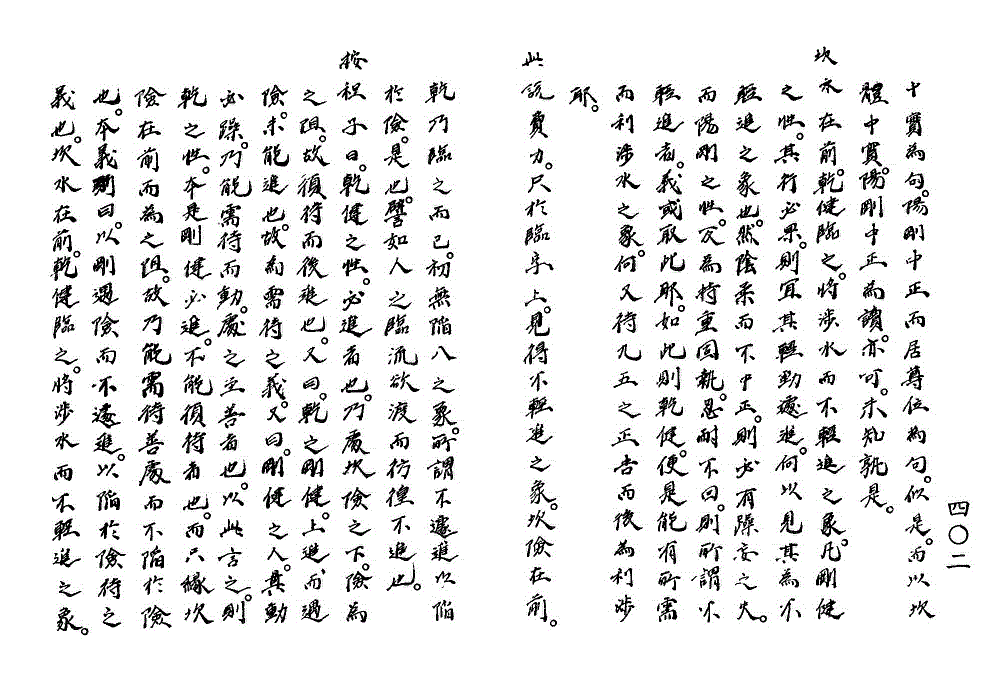 中实为句。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句。似是。而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为读。亦可。未知孰是。
中实为句。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句。似是。而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为读。亦可。未知孰是。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凡刚健之性。其行必果。则宜其轻动遽进。何以见其为不轻进之象也。然阴柔而不中正。则必有躁妄之失。而阳刚之性。反为持重固执。忍耐不回。则所谓不轻进者。义或取此耶。如此则乾健。便是能有所需而利涉水之象。何又待九五之正吉而后为利涉耶。
此说费力。只于临字上。见得不轻进之象。坎险在前。乾乃临之而已。初无陷入之象。所谓不遽进以陷于险。是也。譬如人之临流欲渡而彷徨不进也。
按程子曰。乾健之性。必进者也。乃处坎险之下。险为之阻。故须待而后进也。又曰。乾之刚健。上进而遇险。未能进也。故为需待之义。又曰。刚健之人。其动必躁。乃能需待而动。处之至善者也。以此言之。则乾之性。本是刚健必进。不能须待者也。而只缘坎险在前而为之阻。故乃能需待善处而不陷于险也。本义则曰。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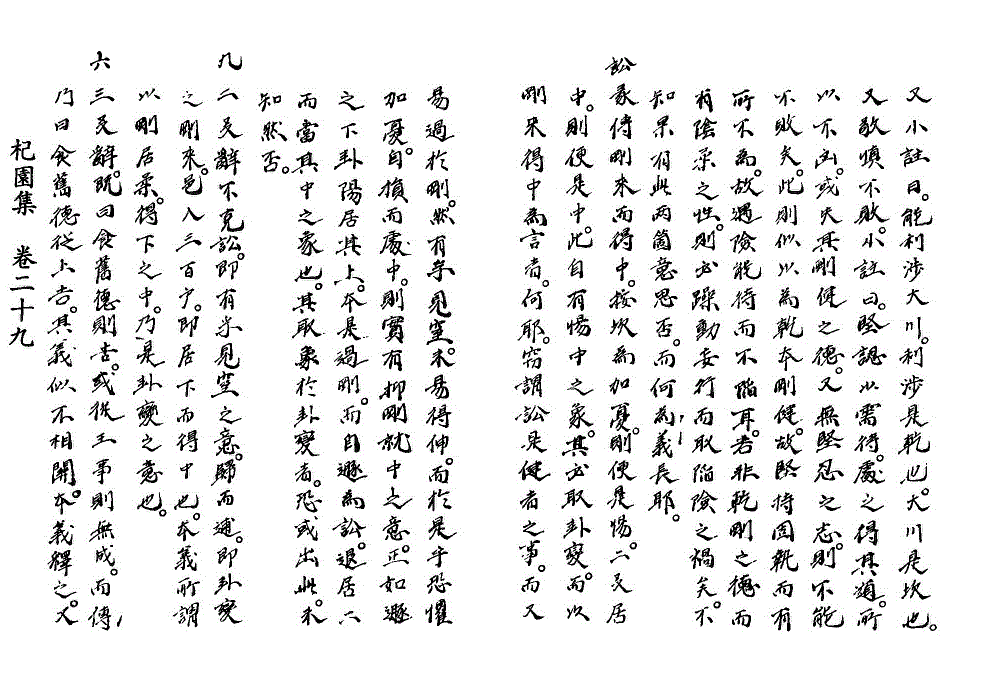 又小注曰。能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又敬慎不败。小注曰。坚认以需待。处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刚健之德。又无坚忍之志。则不能不败矣。此则似以为乾本刚健。故坚持固执而有所不为。故遇险能待而不陷耳。若非乾刚之德而有阴柔之性。则必躁动妄行而取陷险之祸矣。不知果有此两个意思否。而何义为长耶。
又小注曰。能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又敬慎不败。小注曰。坚认以需待。处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刚健之德。又无坚忍之志。则不能不败矣。此则似以为乾本刚健。故坚持固执而有所不为。故遇险能待而不陷耳。若非乾刚之德而有阴柔之性。则必躁动妄行而取陷险之祸矣。不知果有此两个意思否。而何义为长耶。讼彖传刚来而得中。按坎为加忧。则便是惕。二爻居中。则便是中。此自有惕中之象。其必取卦变。而以刚来得中为言者。何耶。窃谓讼是健者之事。而又易过于刚。然有孚见窒。未易得伸。而于是乎恐惧加忧。自损而处中。则实有抑刚就中之意。正如遁之下卦阳居其上。本是过刚。而自遁为讼。退居二而当其中之象也。其取象于卦变者。恐或出此。未知然否。
九二爻辞不克讼。即有孚见窒之意。归而逋。即卦变之刚来。邑人三百户。即居下而得中也。本义所谓以刚居柔。得下之中。乃是卦变之意也。
六三爻辞。既曰食旧德则吉。或从王事则无成。而传乃曰食旧德从上吉。其义似不相关。本义释之。又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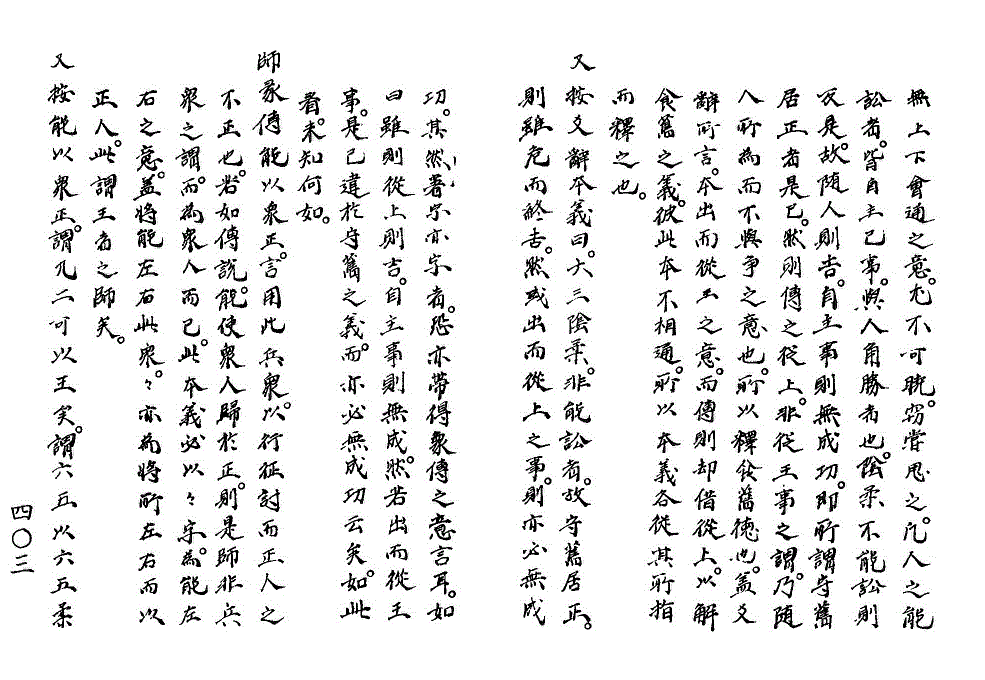 无上下会通之意。尤不可晓。窃尝思之。凡人之能讼者。皆自主己事。与人角胜者也。阴柔不能讼则反是。故随人则吉。自主事则无成功。即所谓守旧居正者是已。然则传之从上。非从王事之谓。乃随人所为而不与争之意也。所以释食旧德也。盖爻辞所言。本出而从王之意。而传则却借从上。以解食旧之义。彼此本不相通。所以本义各从其所指而释之也。
无上下会通之意。尤不可晓。窃尝思之。凡人之能讼者。皆自主己事。与人角胜者也。阴柔不能讼则反是。故随人则吉。自主事则无成功。即所谓守旧居正者是已。然则传之从上。非从王事之谓。乃随人所为而不与争之意也。所以释食旧德也。盖爻辞所言。本出而从王之意。而传则却借从上。以解食旧之义。彼此本不相通。所以本义各从其所指而释之也。又按爻辞本义曰。六三阴柔。非能讼者。故守旧居正。则虽危而终吉。然或出而从上之事。则亦必无成功。其著然字亦字者。恐亦带得象传之意言耳。如曰虽则从上则吉。自主事则无成。然若出而从王事。是已违于守旧之义。而亦必无成功云矣。如此看。未知何如。
师彖传能以众正。言用此兵众。以行征讨而正人之不正也。若如传说。能使众人归于正。则是师非兵众之谓。而为众人而已。此本义必以以字。为能左右之意。盖将能左右此众。众亦为将所左右而以正人。此谓王者之师矣。
又按能以众正。谓九二可以王矣。谓六五以六五柔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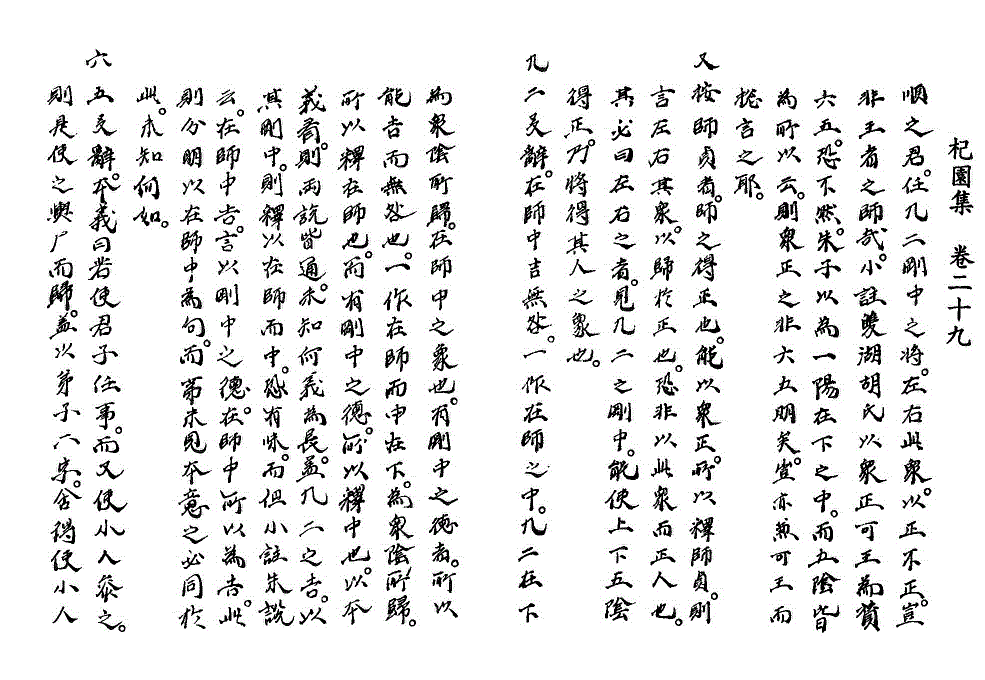 顺之君。任九二刚中之将。左右此众。以正不正。岂非王者之师哉。小注双湖胡氏以众正可王为赞六五。恐不然。朱子以为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云。则众正之非六五明矣。岂亦兼可王而总言之耶。
顺之君。任九二刚中之将。左右此众。以正不正。岂非王者之师哉。小注双湖胡氏以众正可王为赞六五。恐不然。朱子以为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云。则众正之非六五明矣。岂亦兼可王而总言之耶。又按师贞者。师之得正也。能以众正。所以释师贞。则言左右其众。以归于正也。恐非以此众而正人也。其必曰左右之者。见九二之刚中。能使上下五阴得正。乃将得其人之象也。
九二爻辞。在师中吉无咎。一作在师之中。九二在下为众阴所归。在师中之象也。有刚中之德者。所以能吉而无咎也。一作在师而中在下。为众阴所归。所以释在师也。而有刚中之德。所以释中也。以本义看。则两说皆通。未知何义为长。盖九二之吉。以其刚中。则释以在师而中。恐有味。而但小注朱说云。在师中吉。言以刚中之德。在师中所以为吉。此则分明以在师中为句。而第未见本意之必同于此。未知何如。
六五爻辞。本义曰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是使之舆尸而归。盖以弟子二字。含得使小人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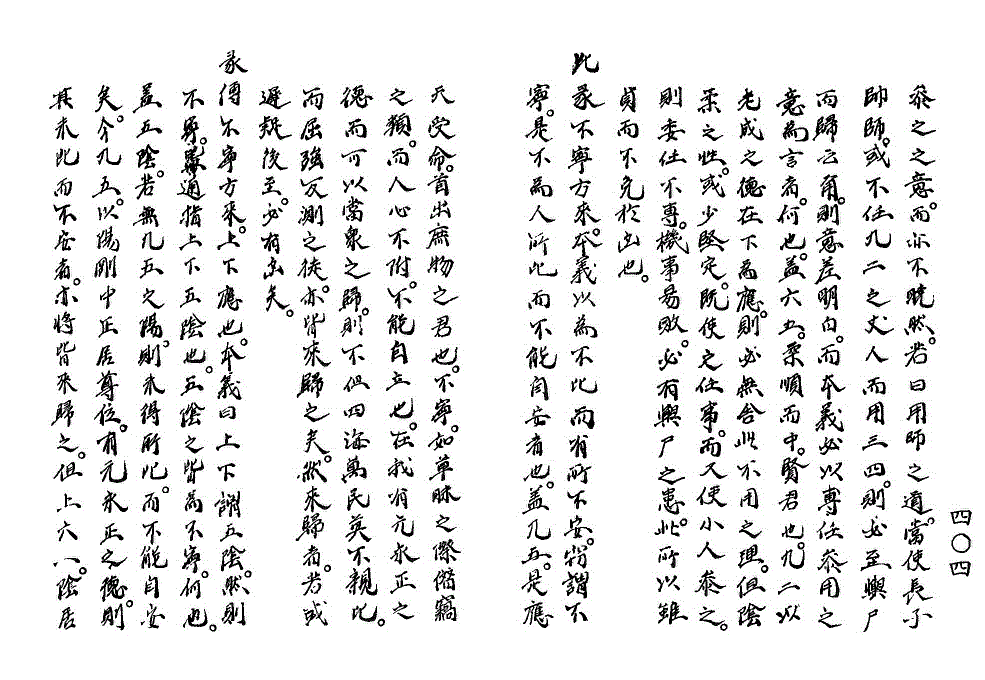 参之之意。而亦不晓然。若曰用师之道。当使长子帅师。或不任九二之丈人而用三四。则必至舆尸而归云尔。则意差明白。而本义必以专任参用之意为言者。何也。盖六五。柔顺而中。贤君也。九二以老成之德在下为应。则必无舍此不用之理。但阴柔之性。或少坚定。既使之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委任不专。机事易败。必有舆尸之患。此所以虽贞而不免于凶也。
参之之意。而亦不晓然。若曰用师之道。当使长子帅师。或不任九二之丈人而用三四。则必至舆尸而归云尔。则意差明白。而本义必以专任参用之意为言者。何也。盖六五。柔顺而中。贤君也。九二以老成之德在下为应。则必无舍此不用之理。但阴柔之性。或少坚定。既使之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委任不专。机事易败。必有舆尸之患。此所以虽贞而不免于凶也。比彖不宁方来。本义以为不比而有所不安。窃谓不宁。是不为人所比而不能自安者也。盖九五。是应天受命。首出庶物之君也。不宁。如草昧之际僭窃之类。而人心不附。不能自立也。在我有元永正之德而可以当众之归。则不但四海万民莫不亲比。而屈强反测之徒。亦皆来归之矣。然来归者。若或迟疑后至。必有凶矣。
彖传不宁方来。上下应也。本义曰上下谓五阴。然则不宁。盖通指上下五阴也。五阴之皆为不宁。何也。盖五阴。若无九五之阳。则未得所比。而不能自安矣。今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有元永正之德。则其未比而不安者。亦将皆来归之。但上六一。阴居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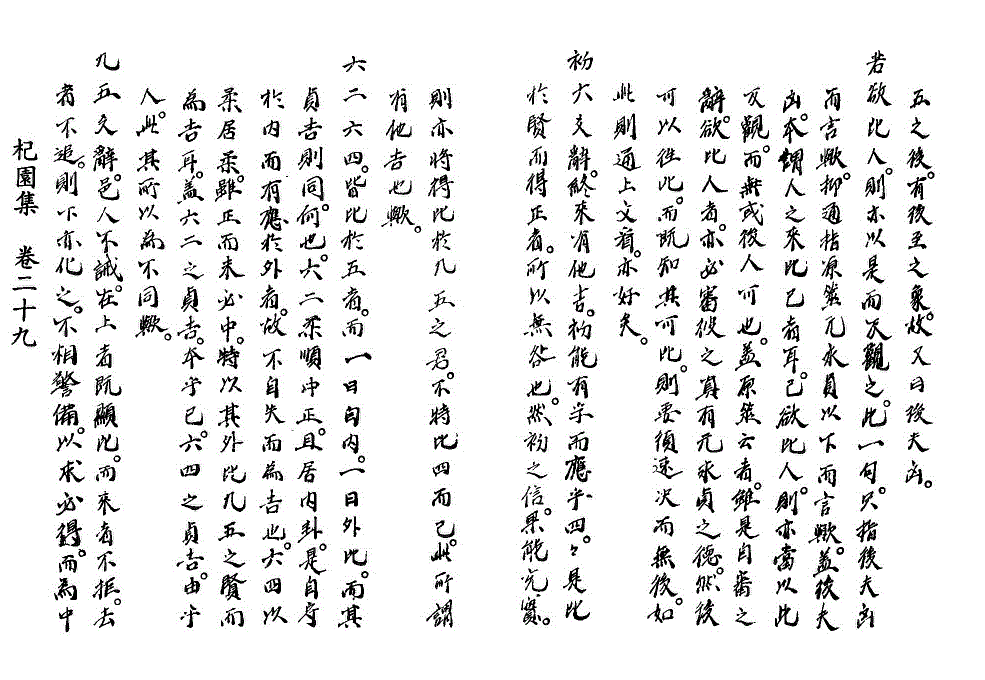 五之后。有后至之象。故又曰后夫凶。
五之后。有后至之象。故又曰后夫凶。若欲比人。则亦以是而反观之。此一句。只指后夫凶而言欤。抑通指原筮元永贞以下而言欤。盖后夫凶。本谓人之来比己者耳。己欲比人。则亦当以此反观。而无或后人可也。盖原筮云者。虽是自审之辞。欲比人者。亦必审彼之真有元永贞之德。然后可以往比。而既知其可比。则要须速决而无后。如此则通上文看。亦好矣。
初六爻辞。终来有他吉。初能有孚而应乎四。四是比于贤而得正者。所以无咎也。然初之信。果能充实。则亦将得比于九五之君。不特比四而已。此所谓有他吉也欤。
六二六四。皆比于五者。而一曰自内。一曰外比。而其贞吉则同。何也。六二柔顺中正。且居内卦。是自守于内而有应于外者。故不自失而为吉也。六四以柔居柔。虽正而未必中。特以其外比九五之贤而为吉耳。盖六二之贞吉。本乎己。六四之贞吉。由乎人。此其所以为不同欤。
九五爻辞。邑人不诫。在上者既显比。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则下亦化之。不相警备。以求必得。而为中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5L 页
 正之德矣。象传所谓上使中者。亦谓此欤。
正之德矣。象传所谓上使中者。亦谓此欤。小畜卦下程传。唯能以巽顺。柔其刚健。柔字。恐畜之误。而他本亦然。下文小注云峰说亦曰。能以巽人柔其刚健。不容皆误。柔恐当作扰系之意看耳。
小畜之象。有二马。以巽畜乾也。以一阴畜五阳也。以巽畜乾。则巽之二阳一阴。皆畜乾之三阳者也。以一阴畜五阳。则上下皆见畜于六四者也。九五上九两爻。传义取象各不同。传则以其见畜于六四者言之。义则以其与四同力畜乾者言之。
彖辞本义。释此二句。似与程传不同。盖密云阴物。西方阴方。云起于西而不能成雨。以阴畜阳不住。是小畜之象也。文王是臣岐周在西。是亦阴也。文王自西而来。不能畜纣之恶。亦小畜之象也。文王演易羑里。以密云自西。系小畜之辞。而默有感于自己之事也。故曰自我西郊。犹有自我西郊而来者为阴。不能畜阳云尔。故言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周为西方。正小畜之时也。盖密云不雨。自是阴微阳盛之致。以其自西郊而然也。只曰自彼西郊可矣。而必曰自我西郊者。其意深矣。故彖传亦曰。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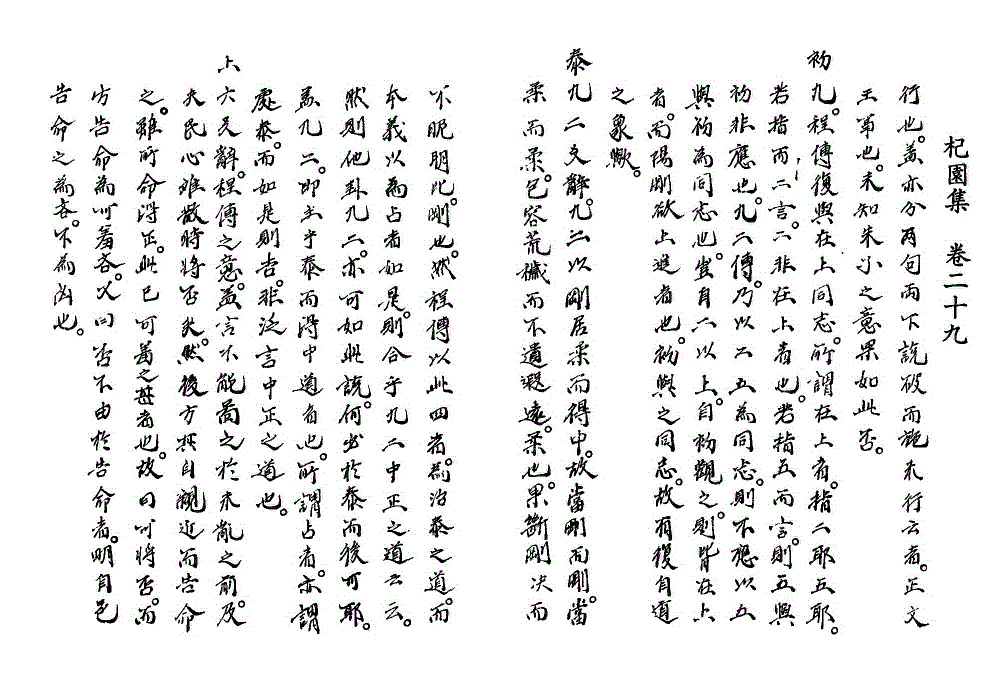 行也。盖亦分两句两下说破而施未行云者。正文王事也。未知朱子之意果如此否。
行也。盖亦分两句两下说破而施未行云者。正文王事也。未知朱子之意果如此否。初九。程传复与在上同志。所谓在上者。指二耶五耶。若指二而言。二非在上者也。若指五而言。则五与初非应也。九二传。乃以二五为同志。则不应以五与初为同志也。岂自二以上。自初观之。则皆在上者。而阳刚欲上进者也。初与之同志。故有复自道之象欤。
泰九二爻辞。九二以刚居柔而得中。故当刚而刚。当柔而柔。包容荒秽而不遗遐远。柔也。果断刚决而不昵朋比。刚也。然程传以此四者。为治泰之道。而本义以为占者如是。则合乎九二中正之道云云。然则他卦九二。亦可如此说。何必于泰而后可耶。盖九二。即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所谓占者。亦谓处泰。而如是则吉。非泛言中正之道也。
上六爻辞。程传之意。盖言不能啚之于未乱之前。及夫民心离散时将否矣。然后方其自亲近而告命之。虽所命得正。此已可羞之甚者也。故曰可将否。而方告命为可羞吝。又曰否不由于告命者。明自邑告命之为吝。不为凶也。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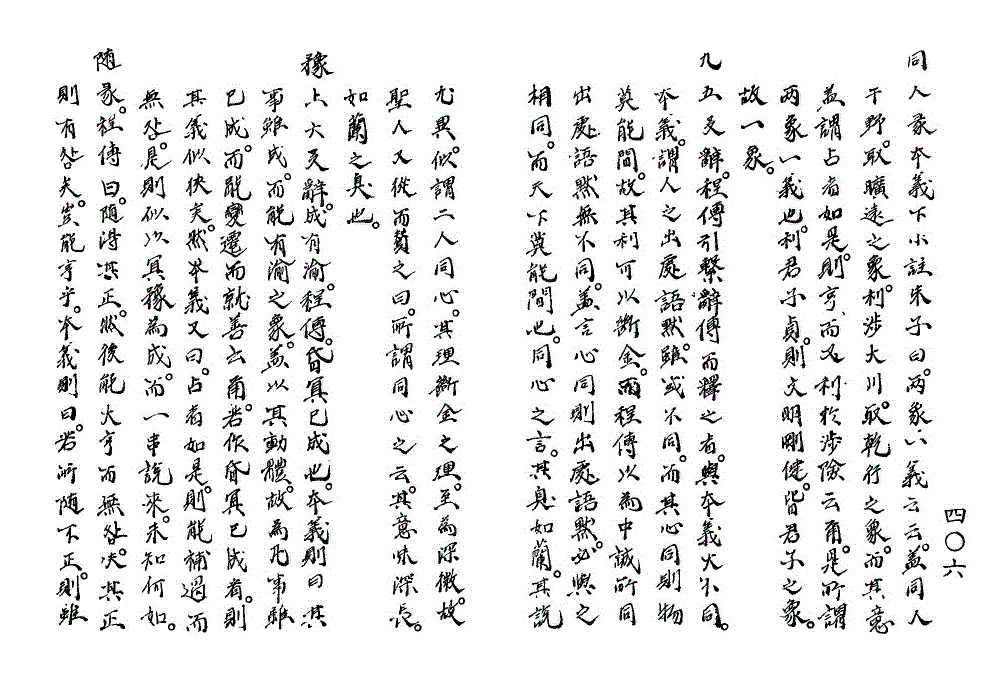 同人彖本义下小注朱子曰。两象一义云云。盖同人干野。取旷远之象。利涉大川。取乾行之象。而其意盖谓占者如是。则亨而又利于涉险云尔。是所谓两象一义也。利君子贞。则文明刚健。皆君子之象。故一象。
同人彖本义下小注朱子曰。两象一义云云。盖同人干野。取旷远之象。利涉大川。取乾行之象。而其意盖谓占者如是。则亨而又利于涉险云尔。是所谓两象一义也。利君子贞。则文明刚健。皆君子之象。故一象。九五爻辞。程传引系辞传而释之者。与本义大不同。本义。谓人之出处语默。虽或不同。而其心同则物莫能间。故其利可以断金。而程传以为中诚所同出处语默无不同。盖言心同则出处语默。必与之相同。而天下莫能间也。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其说尤异。似谓二人同心。其理断金之理。至为深微。故圣人又从而赞之曰。所谓同心之云。其意味深长。如兰之臭也。
豫上六爻辞。成有渝。程传。昏冥已成也。本义则曰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盖以其动体。故为凡事虽已成。而能变迁而就善云尔。若作昏冥已成看。则其义似狭矣。然本义又曰。占者如是。则能补过而无咎。是则似以冥豫为成。而一串说来。未知何如。
随彖。程传曰。随得其正。然后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则有咎矣。岂能亨乎。本义则曰。若所随不正。则虽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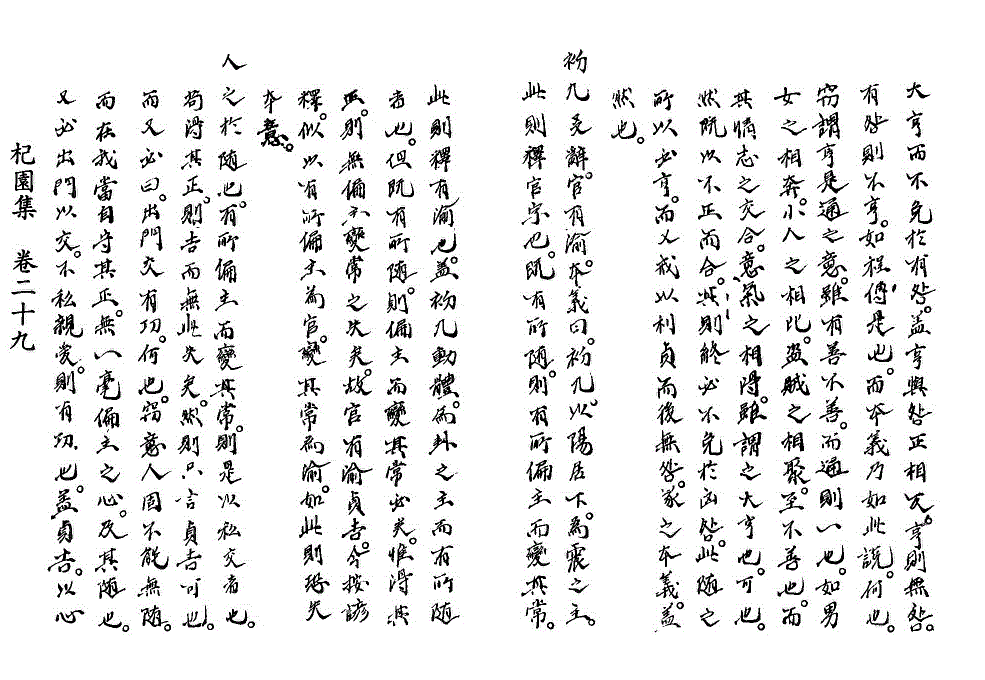 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盖亨与咎正相反。亨则无咎。有咎则不亨。如程传是也。而本义乃如此说。何也。窃谓亨是通之意。虽有善不善。而通则一也。如男女之相奔。小人之相比。盗贼之相聚。至不善也。而其情志之交合。意气之相得。虽谓之大亨也。可也。然既以不正而合。则其终必不免于凶咎。此随之所以必亨。而又戒以利贞而后无咎。彖之本义。盖然也。
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盖亨与咎正相反。亨则无咎。有咎则不亨。如程传是也。而本义乃如此说。何也。窃谓亨是通之意。虽有善不善。而通则一也。如男女之相奔。小人之相比。盗贼之相聚。至不善也。而其情志之交合。意气之相得。虽谓之大亨也。可也。然既以不正而合。则其终必不免于凶咎。此随之所以必亨。而又戒以利贞而后无咎。彖之本义。盖然也。初九爻辞。官有渝。本义曰。初九。以阳居下。为震之主。此则释官字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变其常。此则释有渝也。盖初九动体。为卦之主而有所随者也。但既有所随。则偏主而变其常必矣。惟得其正。则无偏主变常之失矣。故官有渝贞吉。今按谚释。似以有所偏主为官。变其常为渝。如此则恐失本意。
人之于随也。有所偏主而变其常。则是以私交者也。苟得其正。则吉而无此失矣。然则只言贞吉可也。而又必曰。出门交有功。何也。窃意人固不能无随。而在我当自守其正。无一毫偏主之心。及其随也。又必出门以交。不私亲爱。则有功也。盖贞吉。以心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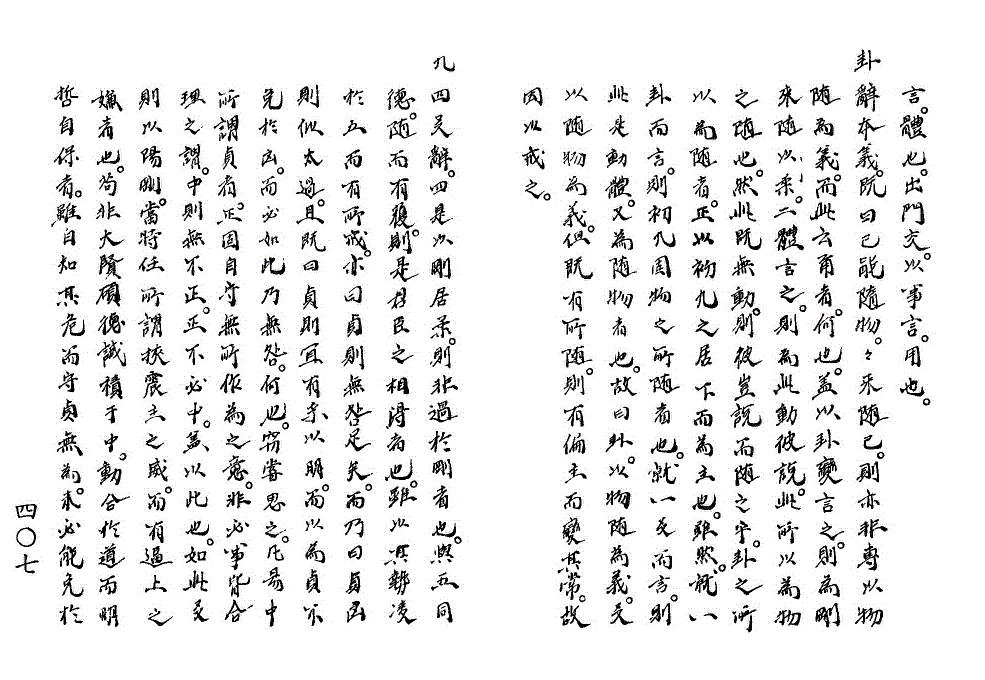 言。体也。出门交。以事言。用也。
言。体也。出门交。以事言。用也。卦辞本义。既曰己能随物。物来随己。则亦非专以物随为义。而此云尔者。何也。盖以卦变言之。则为刚来随柔。以二体言之。则为此动彼说。此所以为物之随也。然此既无动。则彼岂说而随之乎。卦之所以为随者。正以初九之居下而为主也。虽然。就一卦而言。则初九固物之所随者也。就一爻而言。则此是动体。又为随物者也。故曰卦。以物随为义。爻以随物为义。但既有所随。则有偏主而变其常。故因以戒之。
九四爻辞。四是以刚居柔。则非过于刚者也。与五同德。随而有获。则是君臣之相得者也。虽以其势凌于五而有所戒。亦曰贞则无咎足矣。而乃曰贞凶则似太过。且既曰贞则宜有孚以明。而以为贞不免于凶。而必如此乃无咎。何也。窃尝思之。凡易中所谓贞者。正固自守无所作为之意。非必事皆合理之谓。中则无不正。正不必中。盖以此也。如此爻则以阳刚。当时任所谓挟震主之威。而有逼上之嫌者也。苟非大贤硕德诚积于中。动合于道而明哲自保者。虽自知其危而守贞无为。未必能免于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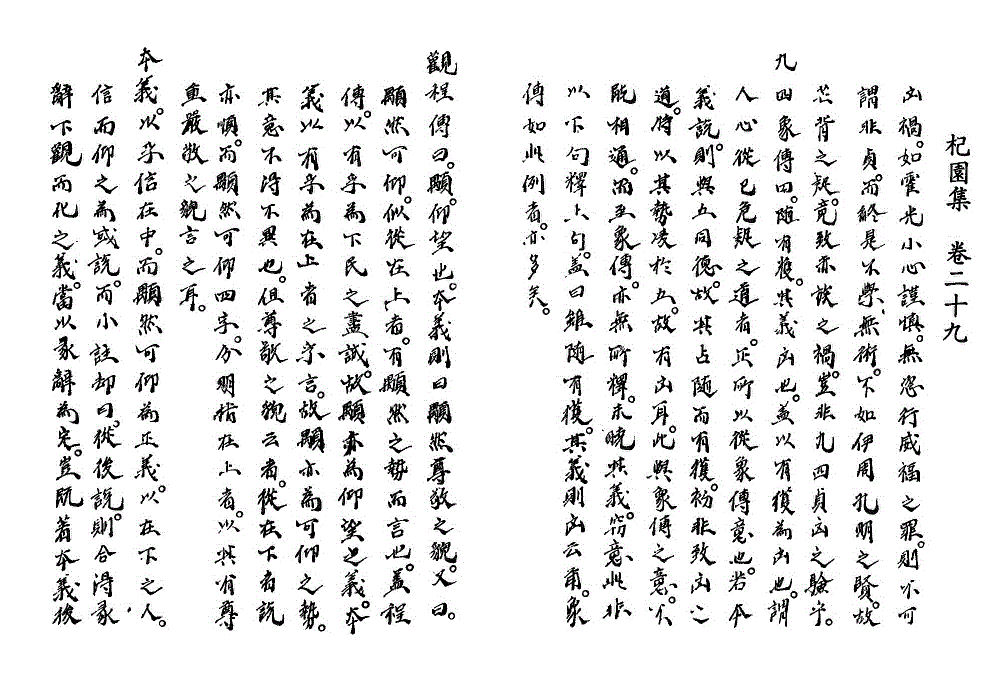 凶祸。如霍光小心谨慎。无恣行威福之罪。则不可谓非贞。而终是不学无术。不如伊周孔明之贤。故芒背之疑。竟致赤族之祸。岂非九四贞凶之验乎。
凶祸。如霍光小心谨慎。无恣行威福之罪。则不可谓非贞。而终是不学无术。不如伊周孔明之贤。故芒背之疑。竟致赤族之祸。岂非九四贞凶之验乎。九四象传曰。随有获。其义凶也。盖以有获为凶也。谓人心从己危疑之道者。正所以从象传意也。若本义说。则与五同德。故其占随而有获。初非致凶之道。特以其势凌于五。故有凶耳。此与象传之意。不能相通。而至象传。亦无所释。未晓其义。窃意此非以下句释上句。盖曰虽随有获。其义则凶云尔。象传如此例者。亦多矣。
观程传曰。颙。仰望也。本义则曰颙然尊敬之貌。又曰。颙然可仰。似从在上者。有颙然之势而言也。盖程传。以有孚为下民之尽诚。故颙亦为仰望之义。本义以有孚为在上者之孚言。故颙亦为可仰之势。其意不得不异也。但尊敬之貌云者。从在下者说亦顺。而颙然可仰四字。分明指在上者。以其有尊重严敬之貌言之耳。
本义。以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为正义。以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为或说。而小注却曰。从后说。则合得彖辞下观而化之义。当以彖辞为定。岂既著本义后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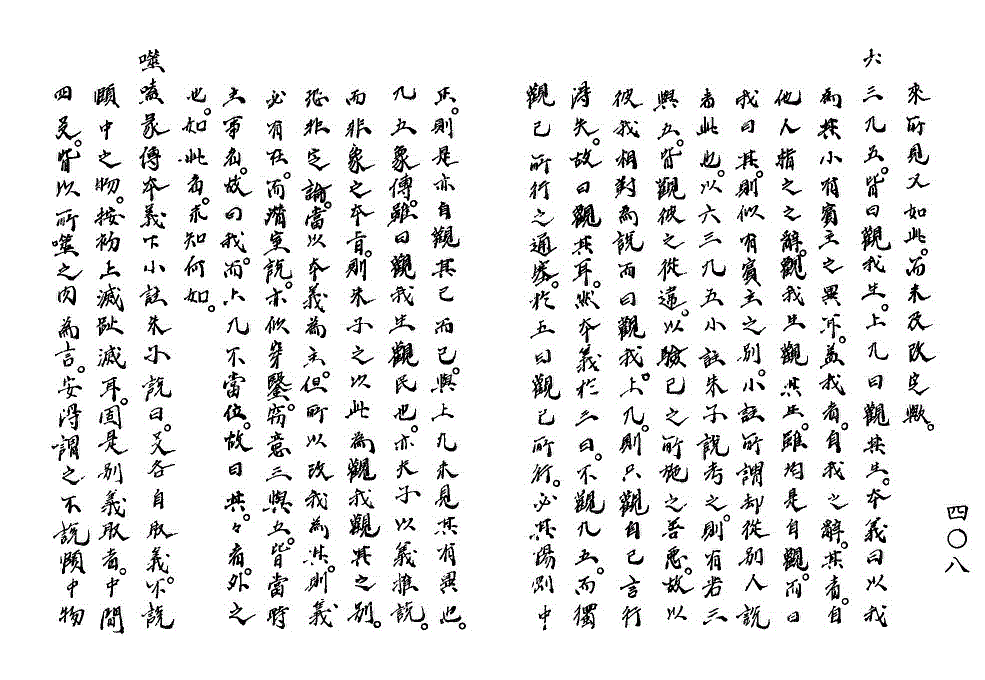 来所见又如此。而未及改定欤。
来所见又如此。而未及改定欤。六三九五。皆曰观我生。上九曰观其生。本义曰以我为其小有宾主之异耳。盖我者。自我之辞。其者。自他人指之之辞。观我生观其生。虽均是自观。而曰我曰其。则似有宾主之别。小注所谓却从别人说者此也。以六三九五小注朱子说考之。则有若三与五。皆观彼之从违。以验己之所施之善恶。故以彼我相对为说而曰观我。上九。则只观自己言行得失。故曰观其耳。然本义于三曰。不观九五。而独观己所行之通塞。于五曰观己所行。必其阳刚中正。则是亦自观其己而已。与上九未见其有异也。九五象传。虽曰观我生观民也。亦夫子以义推说。而非象之本旨。则朱子之以此为观我观其之别。恐非定论。当以本义为主。但所以改我为其。则义必有在。而潜室说。亦似穿凿。窃意三与五。皆当时主事者。故曰我。而上九不当位。故曰其。其者。外之也。如此者。未知何如。
噬嗑彖传本义下小注朱子说曰。爻各自取义。不说颐中之物。按初上灭趾灭耳。固是别义取者。中间四爻。皆以所噬之肉为言。安得谓之不说颐中物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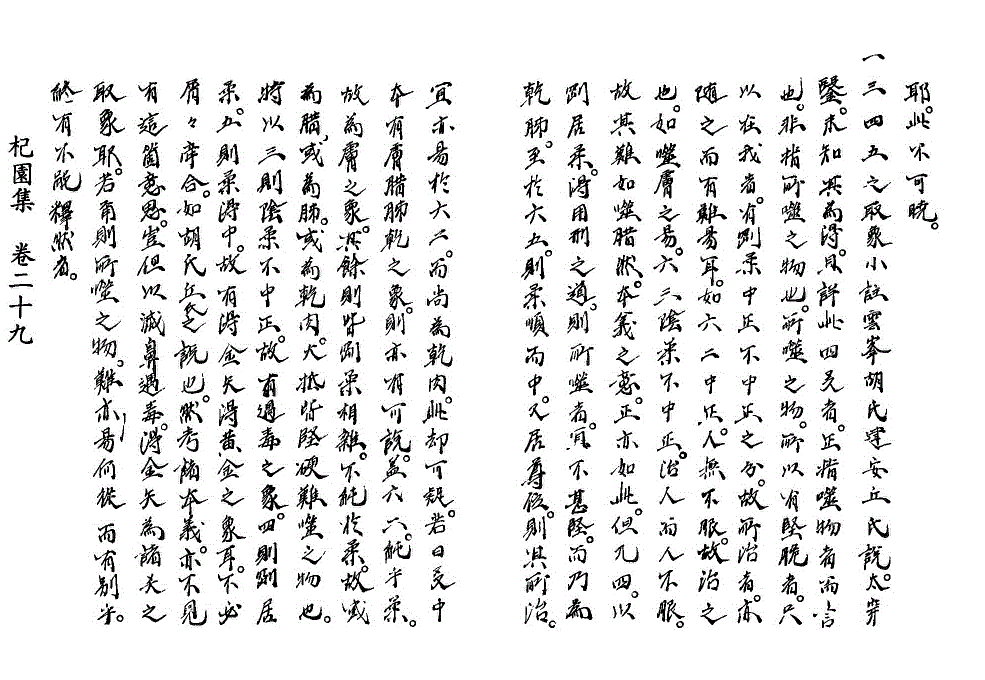 耶。此不可晓。
耶。此不可晓。二三四五之取象小注云峰胡氏建安丘氏说。太穿凿。未知其为得。且详此四爻者。正指噬物者而言也。非指所噬之物也。所噬之物。所以有坚脆者。只以在我者。有刚柔中正不中正之分。故所治者。亦随之而有难易耳。如六二中正。人无不服。故治之也。如噬肤之易。六三阴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故其难如噬腊然。本义之意。正亦如此。但九四。以刚居柔。得用刑之道。则所噬者。宜不甚坚。而乃为乾胏。至于六五。则柔顺而中。又居尊位。则其所治。宜亦易于六二。而尚为乾肉。此却可疑。若曰爻中本有肤腊胏乾之象。则亦有可说。盖六二。纯乎柔。故为肤之象。其馀则皆刚柔相杂。不纯于柔。故或为腊。或为胏。或为乾肉。大抵皆坚硬难噬之物也。特以三则阴柔不中正。故有遇毒之象。四则刚居柔。五则柔得中。故有得金矢得黄金之象耳。不必屑屑牵合。如胡氏丘氏之说也。然考诸本义。亦不见有这个意思。岂但以灭鼻遇毒。得金矢为诸爻之取象耶。若尔则所噬之物。难易亦何从而有别乎。终有不能释然者。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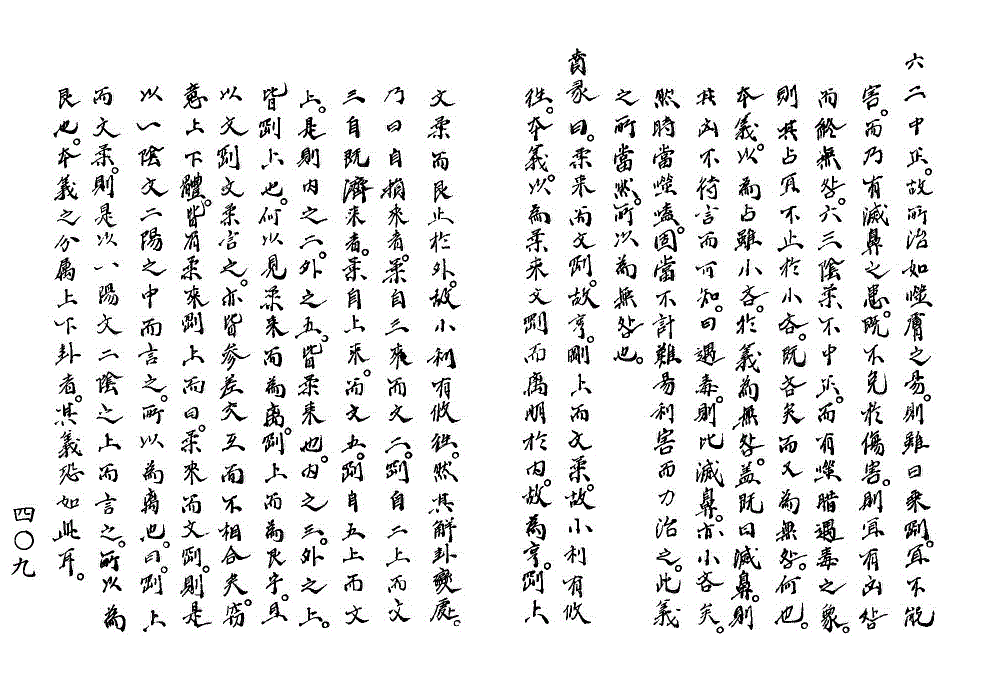 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肤之易。则虽曰乘刚。宜不能害。而乃有灭鼻之患。既不免于伤害。则宜有凶咎而终无咎。六三阴柔不中正。而有噬腊遇毒之象。则其占宜不止于小吝。既吝矣而又为无咎。何也。本义。以为占虽小吝。于义为无咎。盖既曰灭鼻。则其凶不待言而可知。曰遇毒。则比灭鼻。亦小吝矣。然时当噬嗑。固当不计难易利害而力治之。此义之所当然。所以为无咎也。
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肤之易。则虽曰乘刚。宜不能害。而乃有灭鼻之患。既不免于伤害。则宜有凶咎而终无咎。六三阴柔不中正。而有噬腊遇毒之象。则其占宜不止于小吝。既吝矣而又为无咎。何也。本义。以为占虽小吝。于义为无咎。盖既曰灭鼻。则其凶不待言而可知。曰遇毒。则比灭鼻。亦小吝矣。然时当噬嗑。固当不计难易利害而力治之。此义之所当然。所以为无咎也。贲彖曰。柔来而文刚。故亨。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本义。以为柔来文刚而离明于内。故为亨。刚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然其解卦变处。乃曰自损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是则内之二。外之五。皆柔来也。内之三。外之上。皆刚上也。何以见柔来而为离。刚上而为艮乎。且以文刚文柔言之。亦皆参差交互而不相合矣。窃意上下体。皆有柔来刚上而曰。柔来而文刚。则是以一阴文二阳之中而言之。所以为离也。曰。刚上而文柔。则是以一阳文二阴之上而言之。所以为艮也。本义之分属上下卦者。其义恐如此耳。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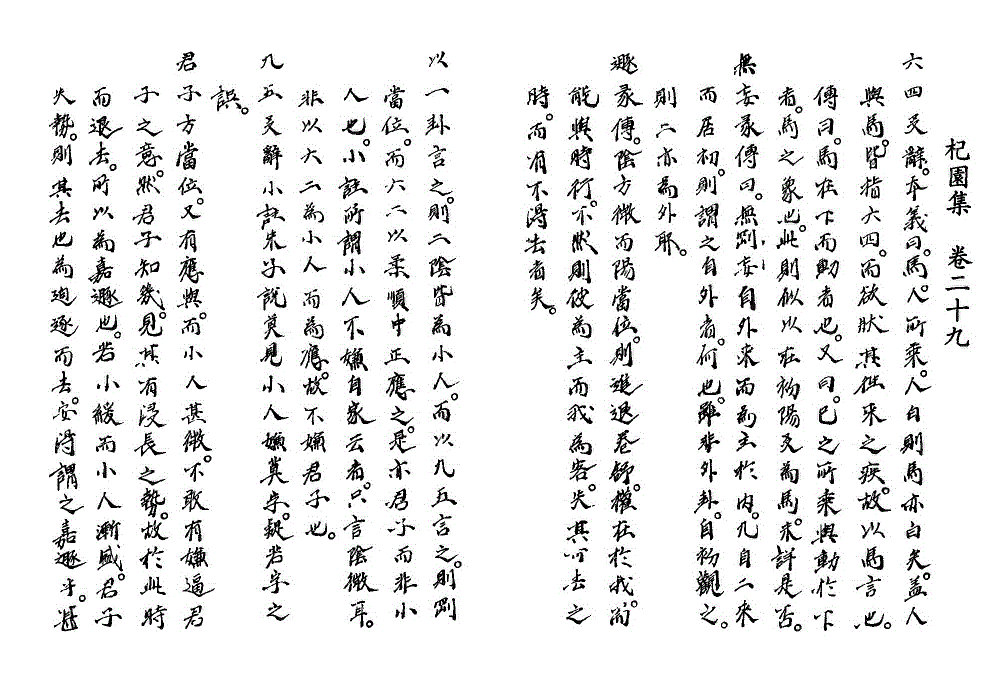 六四爻辞。本义曰。马。人所乘。人白则马亦白矣。盖人与马。皆指六四。而欲状其往来之疾。故以马言也。传曰。马在下而动者也。又曰。己之所乘与动于下者。马之象也。此则似以在初阳爻为马。未详是否。
六四爻辞。本义曰。马。人所乘。人白则马亦白矣。盖人与马。皆指六四。而欲状其往来之疾。故以马言也。传曰。马在下而动者也。又曰。己之所乘与动于下者。马之象也。此则似以在初阳爻为马。未详是否。无妄彖传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九自二来而居初。则谓之自外者。何也。虽非外卦。自初观之。则二亦为外耶。
遁彖传。阴方微而阳当位。则进退卷舒。权在于我。而能与时行。不然则彼为主而我为客。失其可去之时。而有不得去者矣。
以一卦言之。则二阴皆为小人。而以九五言之。则刚当位。而六二以柔顺中正应之。是亦君子而非小人也。小注所谓小人不嫌自家云者。只言阴微耳。非以六二为小人而为应。故不嫌君子也。
九五爻辞小注朱子说莫见小人嫌莫字。疑若字之误。
君子方当位。又有应与。而小人甚微。不敢有嫌逼君子之意。然君子知几。见其有浸长之势。故于此时而退去。所以为嘉遁也。若小缓而小人渐盛。君子失势。则其去也为迫逐而去。安得谓之嘉遁乎。甚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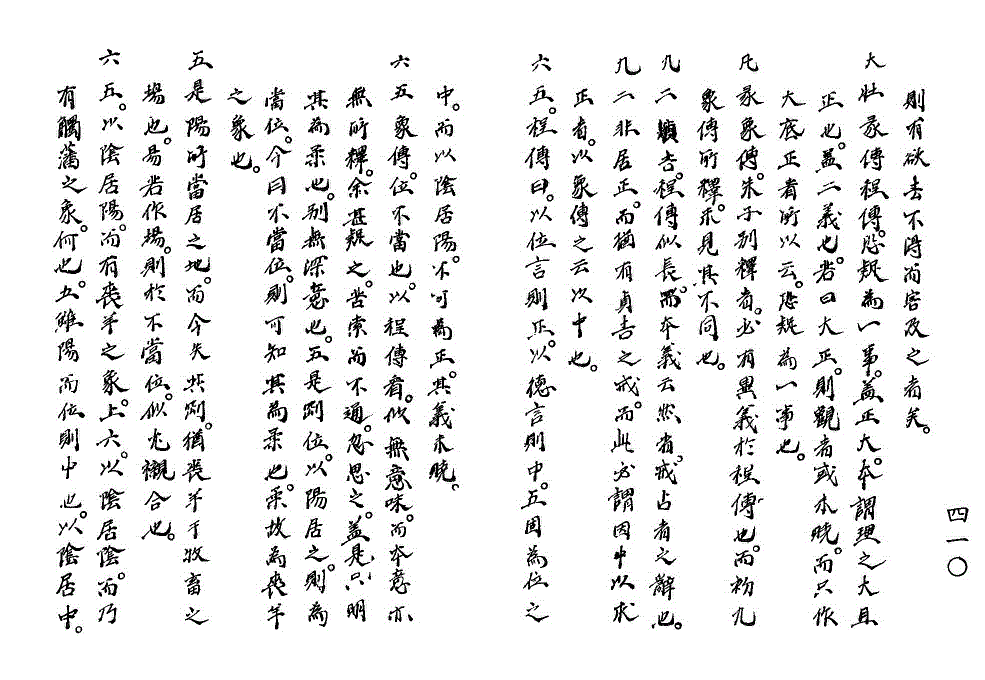 则有欲去不得而害及之者矣。
则有欲去不得而害及之者矣。大壮彖传程传。恐疑为一事。盖正大。本谓理之大且正也。盖二义也。若曰大正。则观者或未晓。而只作大底正看所以云。恐疑为一事也。
凡彖象传。朱子别释者。必有异义于程传也。而初九象传所释。未见其不同也。
九二贞吉。程传似长。而本义云然者。戒占者之辞也。
九二非居正。而犹有贞吉之戒。而此必谓因中以求正者。以象传之云以中也。
六五。程传曰。以位言则正。以德言则中。五固为位之中。而以阴居阳。不可为正。其义未晓。
六五象传。位不当也。以程传看。似无意味。而本意亦无所释。余甚疑之。苦索而不通。忽思之。盖只是明其为柔也。别无深意也。五是刚位。以阳居之。则为当位。今曰不当位。则可知其为柔也。柔故为丧羊之象也。
五是阳所当居之地。而今失其刚。犹丧羊于牧畜之场也。易若作场。则于不当位。似尤衬合也。
六五。以阴居阳。而有丧羊之象。上六。以阴居阴。而乃有触藩之象。何也。五虽阳而位则中也。以阴居中。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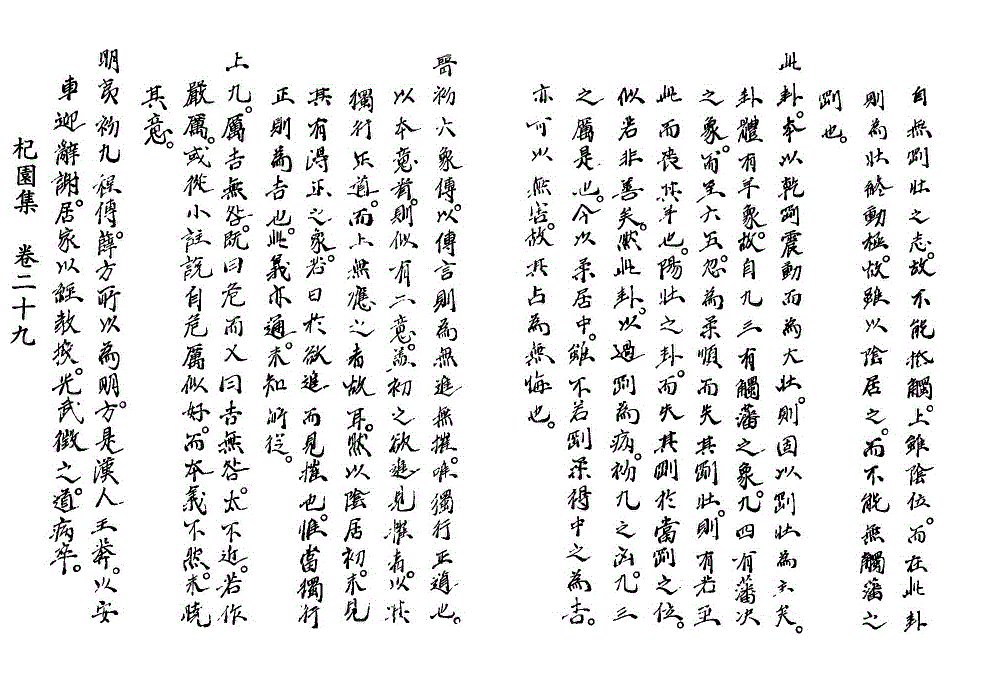 自无刚壮之志。故不能抵触。上虽阴位。而在此卦则为壮终动极。故虽以阴居之。而不能无触藩之刚也。
自无刚壮之志。故不能抵触。上虽阴位。而在此卦则为壮终动极。故虽以阴居之。而不能无触藩之刚也。此卦。本以乾刚震动而为大壮。则固以刚壮为主矣。卦体有羊象。故自九三有触藩之象。九四有藩决之象。而至六五。忽为柔顺而失其刚壮。则有若至此而丧其羊也。阳壮之卦。而失其刚于当刚之位。似若非善矣。然此卦。以过刚为病。初九之凶。九三之厉是也。今以柔居中。虽不若刚柔得中之为吉。亦可以无害。故其占为无悔也。
晋初六象传。以传言则为无进无摧。唯独行正道也。以本意看。则似有二意。盖初之欲进见摧者。以其独行正道。而上无应之者故耳。然以阴居初。未见其有得正之象。若曰于欲进而见摧也。惟当独行正则为吉也。此义亦通。未知所从。
上九。厉吉无咎。既曰危而又曰吉无咎。太不近。若作严厉。或从小注说自危厉似好。而本义不然。未晓其意。
明夷初九程传。薛方所以为明。方是汉人王莽。以安车迎辞谢。居家以经教授。光武徵之。道病卒。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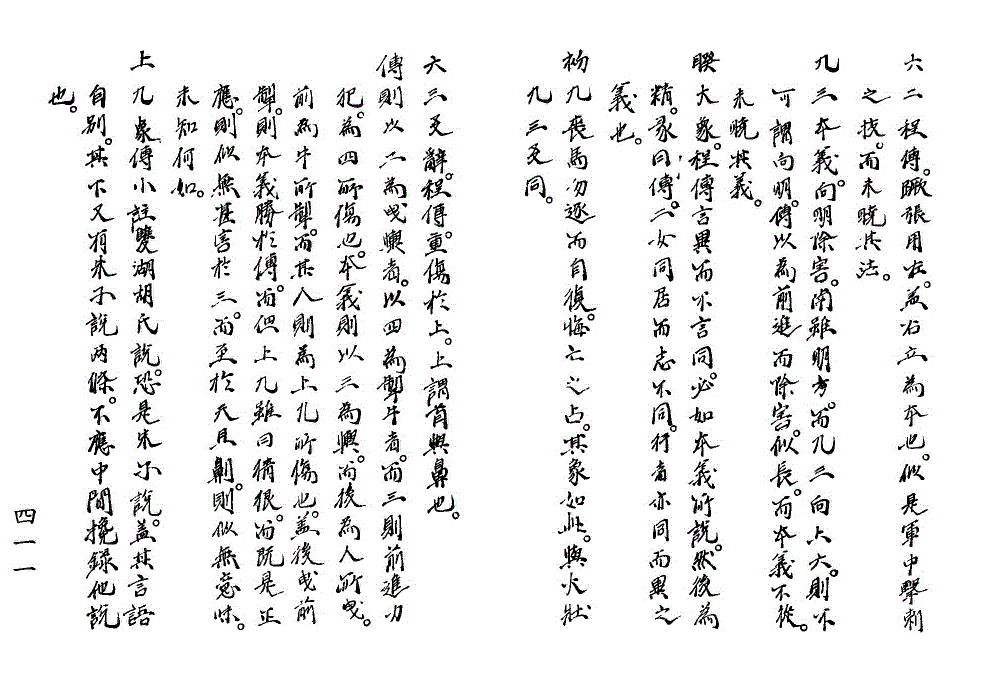 六二程传。蹶张用左。盖右立为本也。似是军中击刺之技。而未晓其法。
六二程传。蹶张用左。盖右立为本也。似是军中击刺之技。而未晓其法。九三本义。向明除害。南虽明方。而九三向上六。则不可谓向明。传以为前进而除害。似长。而本义不从。未晓其义。
睽大象。程传言异而不言同。必如本义所说。然后为精。彖传曰。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亦同而异之义也。
初九丧马勿逐而自复。悔亡之占。其象如此。与大壮九三爻同。
六三爻辞。程传。重伤于上。上谓首与鼻也。
传则以二为曳舆者。以四为掣牛者。而三则前进力犯。为四所伤也。本义则以三为舆。而后为人所曳。前为牛所掣。而其人则为上九所伤也。盖后曳前掣。则本义胜于传。而但上九虽曰猜狠。而既是正应。则似无甚害于三。而至于天且劓。则似无意味。未知何如。
上九象传小注双湖胡氏说。恐是朱子说。盖其言语自别。其下又有朱子说两条。不应中间搀录他说也。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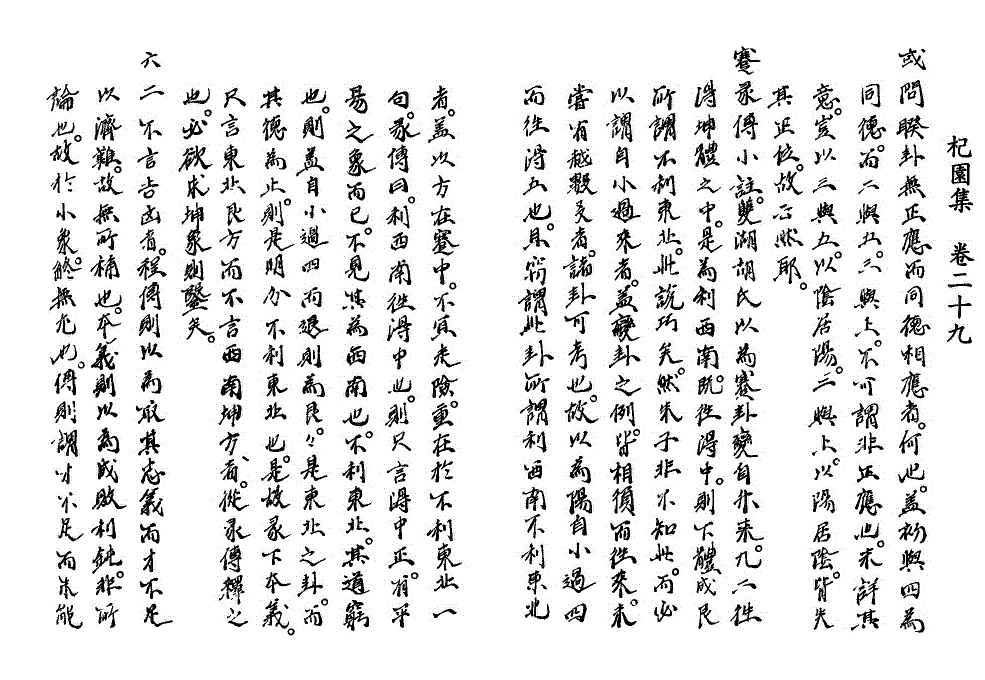 或问睽卦无正应而同德相应者。何也。盖初与四为同德。而二与五。三与上。不可谓非正应也。未详其意。岂以三与五。以阴居阳。二与上。以阳居阴。皆失其正位。故云然耶。
或问睽卦无正应而同德相应者。何也。盖初与四为同德。而二与五。三与上。不可谓非正应也。未详其意。岂以三与五。以阴居阳。二与上。以阳居阴。皆失其正位。故云然耶。蹇彖传小注。双湖胡氏以为蹇卦变自升来。九二往得坤体之中。是为利西南。既往得中。则下体成艮所谓不利东北。此说巧矣。然朱子非不知此。而必以谓自小过来者。盖变卦之例。皆相须而往来。未尝有越数爻者。诸卦可考也。故以为阳自小过四而往得五也。且窃谓此卦所谓利西南不利东北者。盖以方在蹇中。不宜走险。重在于不利东北一句。彖传曰。利西南往得中也。则只言得中正。有平易之象而已。不见其为西南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则盖自小过四而退则为艮。艮是东北之卦。而其德为止。则是明分不利东北也。是故彖下本义。只言东北艮方而不言西南坤方者。从彖传释之也。必欲求坤象则凿矣。
六二不言吉凶者。程传则以为取其志义而才不足以济难。故无所称也。本义则以为成败利钝。非所论也。故于小象。终无尤也。传则谓才不足而未能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2L 页
 济难也。本义所论事虽不济者。乃鞠躬尽力。而不幸而不成功。如孔明之为也。传义所说。自不同也。而云峰以为本程传意。恐不然也。
济难也。本义所论事虽不济者。乃鞠躬尽力。而不幸而不成功。如孔明之为也。传义所说。自不同也。而云峰以为本程传意。恐不然也。解初六之为无咎者。以柔在下而刚阳在上为应也。象传所谓刚柔际者是也。传以为以柔居刚。以阴居阳。柔而能刚之象。自处得刚柔之宜。是则以初六一爻。能兼刚柔之德。于刚柔接之义。恐小异也。
九二取象如此看。似无可疑。而本义以为未详。何也。
九四之象曰未当位。本义以为初与四。皆不得其位而相应。应之不以正者是也。盖四既失其位。而初又以不正应之。故解而去之。不然则交相为助。又何以去之乎。盖兼两爻释之也。程传则以为九四。以刚居柔。不足于正。若复亲比小人。则失正必矣。戒以解其拇。此则专以九四一爻言之也。若以他卦例观之。则未当位。皆指当爻而未有兼及他爻者。本义所释。未知果何如也。
初与四。皆不得其位而相应。应之不以正者也。而初则以刚柔之相际而得无咎。四则以初之非类而解其拇。何也。窃谓以正相应。则阴助阳阳助阴而获吉矣。虽不正。而以在下之阴。从在上之阳。则刚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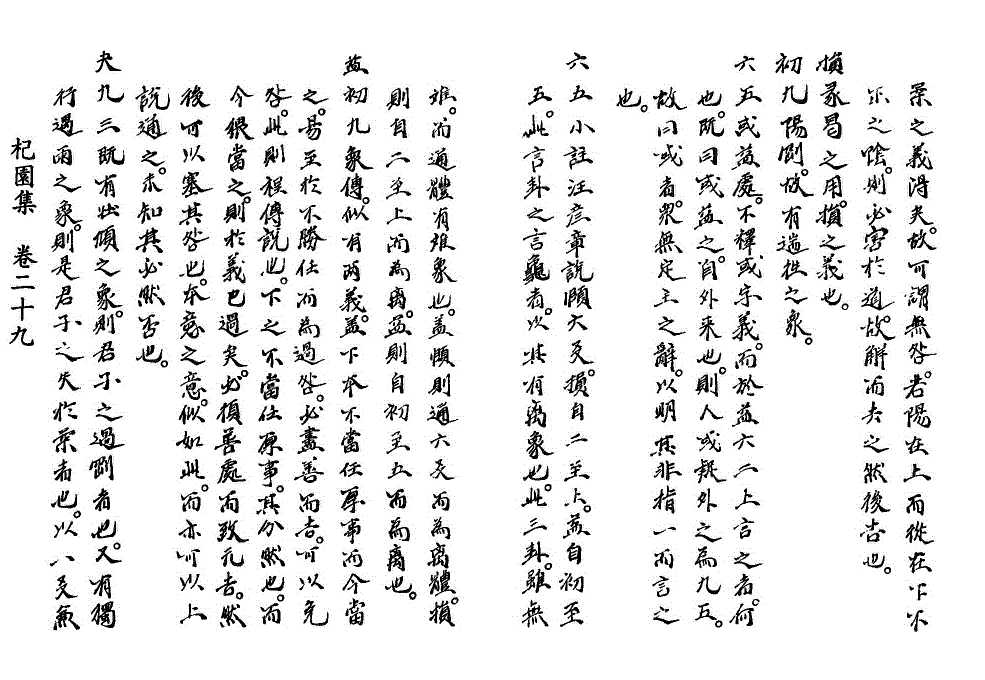 柔之义得矣。故可谓无咎。若阳在上而从在下不正之阴。则必害于道。故解而去之然后吉也。
柔之义得矣。故可谓无咎。若阳在上而从在下不正之阴。则必害于道。故解而去之然后吉也。损彖曷之用。损之义也。
初九阳刚。故有遄往之象。
六五或益处。不释或字义。而于益六二上言之者。何也。既曰或益之。自外来也。则人或疑外之为九五。故曰或者。众无定主之辞。以明其非指一而言之也。
六五小注汪彦章说颐六爻。损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言卦之言龟者。以其有离象也。此三卦。虽无离。而通体有离象也。盖颐则通六爻而为离体。损则自二至上而为离。益则自初至五而为离也。
益初九象传。似有两义。盖下本不当任厚事而今当之。易至于不胜任而为过咎。必尽善而吉。可以免咎。此则程传说也。下之不当任原事。其分然也。而今猥当之。则于义已过矣。必须善处而致元吉。然后可以塞其咎也。本意之意。似如此。而亦可以上说通之。未知其必然否也。
夬九三既有壮倾之象。则君子之过刚者也。又有独行遇雨之象。则是君子之失于柔者也。以一爻兼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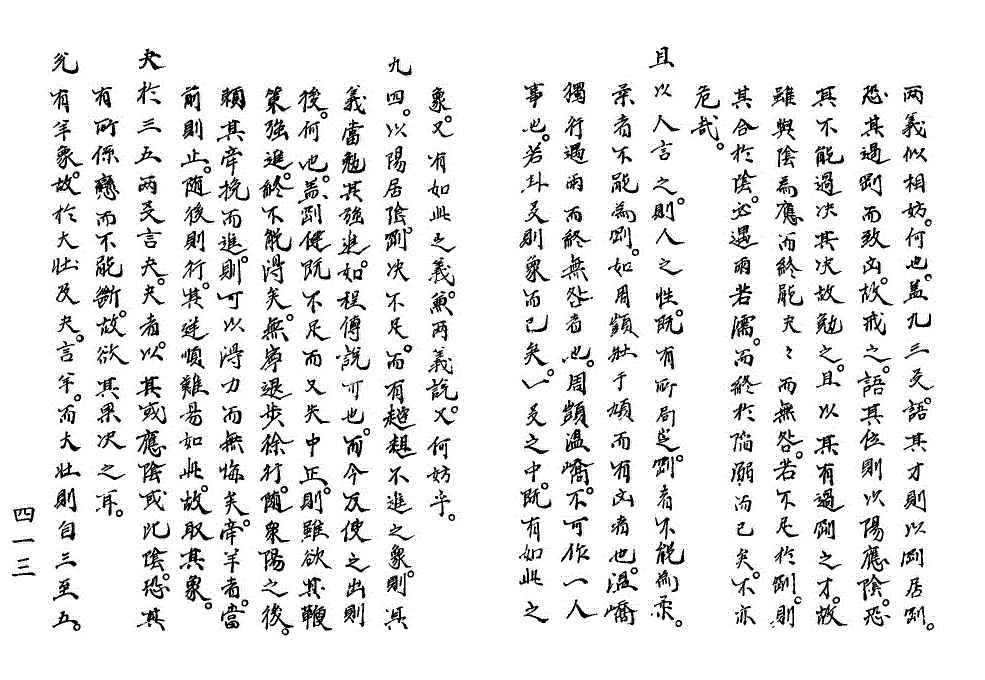 两义似相妨。何也。盖九三爻。语其才则以刚居刚。恐其过刚而致凶。故戒之。语其位则以阳应阴。恐其不能过决其决故勉之。且以其有过刚之才。故虽与阴为应而终能夬夬而无咎。若不足于刚。则其合于阴。必遇雨若濡。而终于陷溺而已矣。不亦危哉。
两义似相妨。何也。盖九三爻。语其才则以刚居刚。恐其过刚而致凶。故戒之。语其位则以阳应阴。恐其不能过决其决故勉之。且以其有过刚之才。故虽与阴为应而终能夬夬而无咎。若不足于刚。则其合于阴。必遇雨若濡。而终于陷溺而已矣。不亦危哉。且以人言之。则人之性。既有所局定。刚者不能为柔。柔者不能为刚。如周顗壮于頄而有凶者也。温峤独行遇雨而终无咎者也。周顗温峤。不可作一人事也。若卦爻则象而已矣。一爻之中。既有如此之象。又有如此之义。兼两义说。又何妨乎。
九四。以阳居阴。刚决不足。而有趑趄不进之象。则其义当勉其强进。如程传说可也。而今反使之出则后。何也。盖刚健既不足而又失中正。则虽欲其鞭策强进。终不能得矣。无宁退步徐行。随众阳之后。赖其牵挽而进。则可以得力而无悔矣。牵羊者。当前则止。随后则行。其逆顺难易如此。故取其象。
夬于三五两爻言夬。夬者。以其或应阴或比阴。恐其有所系恋而不能断。故欲其果决之耳。
兑有羊象。故于大壮及夬。言羊。而大壮则自三至五。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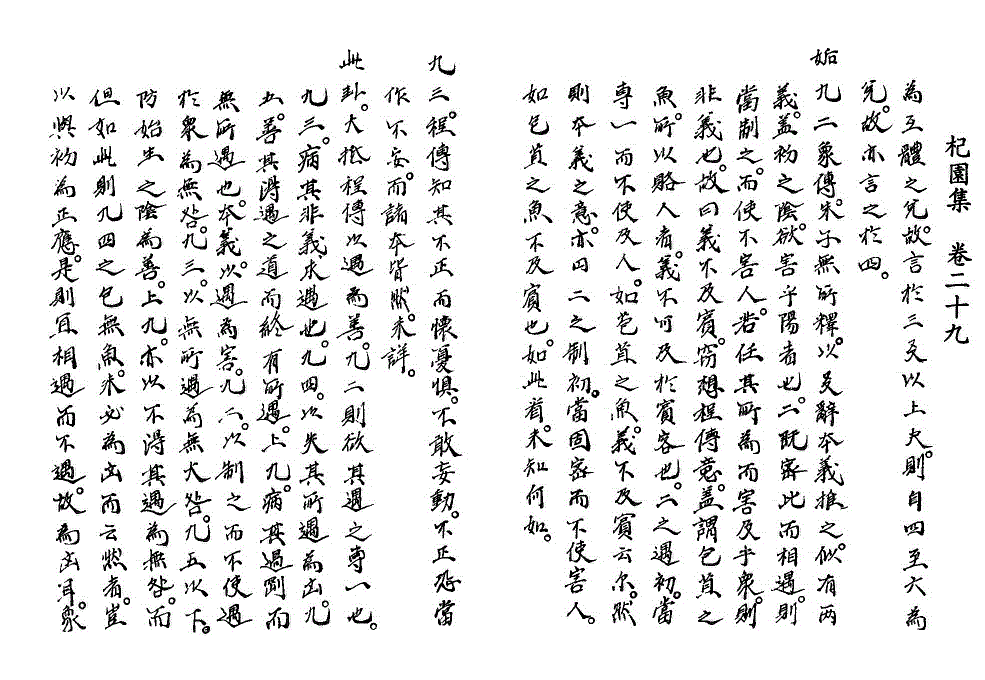 为互体之兑。故言于三爻以上夬。则自四至六为兑。故亦言之于四。
为互体之兑。故言于三爻以上夬。则自四至六为兑。故亦言之于四。姤九二象传。朱子无所释。以爻辞本义推之。似有两义。盖初之阴。欲害乎阳者也。二既密比而相遇。则当制之。而使不害人。若任其所为而害及乎众。则非义也。故曰义不及宾。窃想程传意。盖谓包苴之鱼。所以赂人者。义不可及于宾客也。二之遇初。当专一而不使及人。如苞苴之鱼。义不及宾云尔。然则本义之意。亦曰二之制初。当固密而不使害人。如包苴之鱼不及宾也。如此看。未知何如。
九三。程传知其不正而怀忧惧。不敢妄动。不正恐当作不安。而诸本皆然。未详。
此卦。大抵程传以遇为善。九二则欲其遇之专一也。九三。病其非义求遇也。九四。以失其所遇为凶。九五。善其得遇之道而终有所遇。上九。病其过刚而无所遇也。本义。以遇为害。九二。以制之而不使遇于众为无咎。九三。以无所遇为无大咎。九五以下。防始生之阴为善。上九。亦以不得其遇为无咎。而但如此则九四之包无鱼。未必为凶而云然者。岂以与初为正应。是则宜相遇而不遇。故为凶耳。象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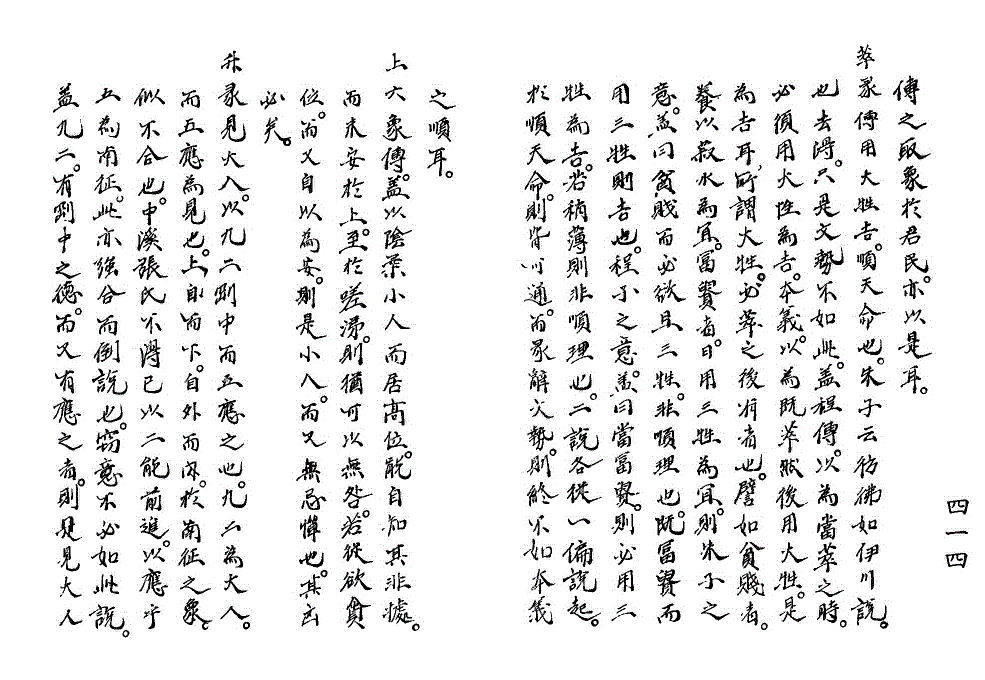 传之取象于君民。亦以是耳。
传之取象于君民。亦以是耳。萃彖传用大牲吉。顺天命也。朱子云彷佛如伊川说。也去得。只是文势不如此。盖程传。以为当萃之时。必须用大牲为吉。本义。以为既萃然后用大牲。是为吉耳。所谓大牲。必萃之后有者也。譬如贫贱者。养以菽水为宜。富贵者。日用三牲为宜。则朱子之意。盖曰贫贱而必欲且三牲。非顺理也。既富贵而用三牲则吉也。程子之意。盖曰当富贵。则必用三牲为吉。若稍薄则非顺理也。二说各从一偏说起。于顺天命。则皆可通。而彖辞文势。则终不如本义之顺耳。
上六象传。盖以阴柔小人而居高位。能自知其非据。而未安于上。至于嗟涕。则犹可以无咎。若从欲贪位。而又自以为安。则是小人。而又无忌惮也。其凶必矣。
升彖见大人。以九二刚中而五应之也。九二为大人。而五应为见也。自上而下。自外而内。于南征之象。似不合也。中溪张氏不得已以二能前进。以应乎五为南征。此亦强合而倒说也。窃意不必如此说。盖九二。有刚中之德。而又有应之者。则是见大人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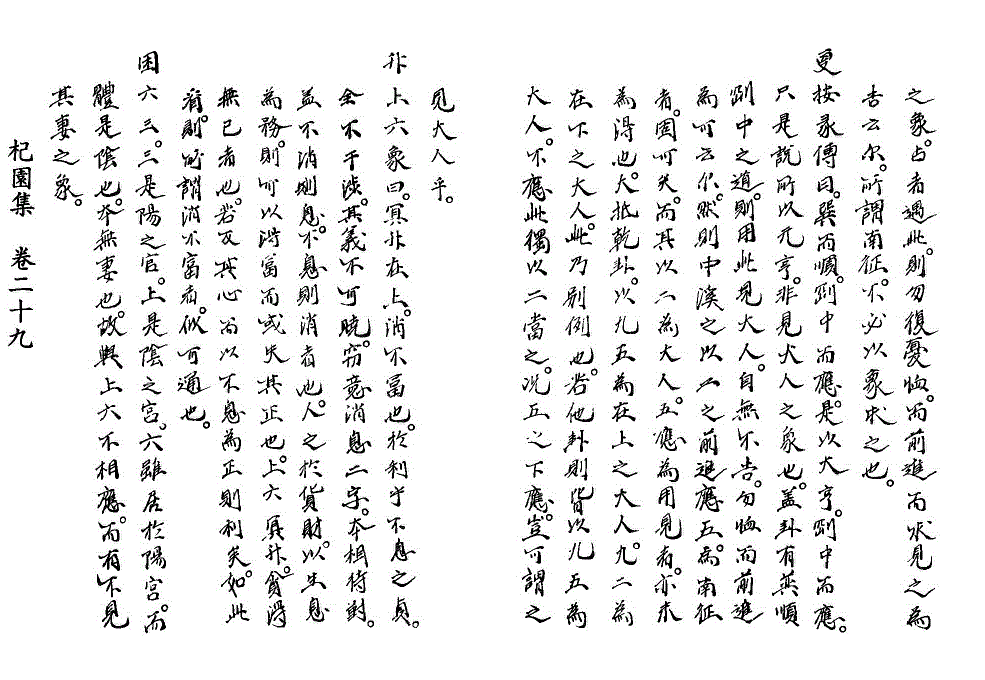 之象。占者遇此。则勿复忧恤。而前进而求见之为吉云尔。所谓南征。不必以象求之也。
之象。占者遇此。则勿复忧恤。而前进而求见之为吉云尔。所谓南征。不必以象求之也。更按彖传曰。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刚中而应。只是说所以元亨。非见大人之象也。盖卦有巽顺刚中之道。则用此见大人。自无不吉。勿恤而前进为可云尔。然则中溪之以二之前进应五。为南征者。固可矣。而其以二为大人。五应为用见者。亦未为得也。大抵乾卦。以九五为在上之大人。九二为在下之大人。此乃别例也。若他卦则皆以九五为大人。不应此独以二当之。况五之下应。岂可谓之见大人乎。
升上六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于利乎不息之贞。全不干涉。其义不可晓。窃意消息二字。本相待对。盖不消则息。不息则消者也。人之于货财。以生息为务。则可以得富而或失其正也。上六冥升。贪得无已者也。若反其心而以不息为正则利矣。如此看。则所谓消不富者。似可通也。
困六三。三是阳之宫。上是阴之宫。六虽居于阳宫。而体是阴也。本无妻也。故与上六不相应。而有不见其妻之象。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5L 页
 九五本义。困下既伤。则赤绂无所用而反为困矣。此一句。不可晓。岂绂所以蔽膝。而既刖之人。虽有绂。亦无所施。若必用之。则反致缠束而为其所困。故云然耶。
九五本义。困下既伤。则赤绂无所用而反为困矣。此一句。不可晓。岂绂所以蔽膝。而既刖之人。虽有绂。亦无所施。若必用之。则反致缠束而为其所困。故云然耶。井彖小注。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意。不取本义。而本义乃曰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出其水。何也。程传盖以木为汲水之器。而与羸其说之说。不相合。故非之。而本义则似取凿井之象。以木克土。而深入乎坎水之下。岂非穴地出水之象乎。但彖传曰。巽乎水而上水。此则只取巽入之义。而本义初不依此作解。而必搀入巽木之说。亦未知其何意也。
初六象传。旧井无禽时舍也。程传。曰人不食则水不上。禽鸟亦不至。见其不能济物。为时所舍置不用也。此盖言旧井无禽。无及物之功。故为时所舍也。本义乃曰。言为时所弃。此则谓旧井无禽。便是为时舍也。不然。似不必别释也。
九三为我心恻。观者自我也。
革彖传本义下小注。朱子说锢露家事。此盖当时俗语。窃意锢者补塞之意。露则器弊而物漏也。家事。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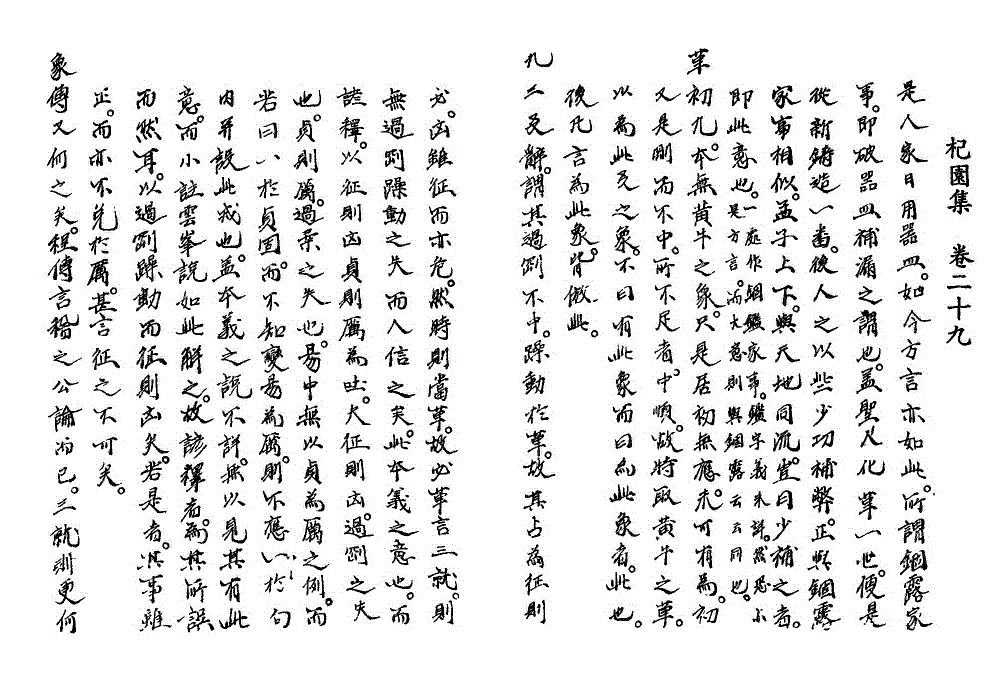 是人家日用器皿。如今方言亦如此。所谓锢露家事。即破器皿补漏之谓也。盖圣人化革一世。便是从新铸造一番。后人之以些少功补弊。正与锢露家事相似。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少补之者。即此意也。(一处作锢鉴家事。鉴字义未详。然恐亦是方言。而大意则与锢露云云同也。)
是人家日用器皿。如今方言亦如此。所谓锢露家事。即破器皿补漏之谓也。盖圣人化革一世。便是从新铸造一番。后人之以些少功补弊。正与锢露家事相似。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少补之者。即此意也。(一处作锢鉴家事。鉴字义未详。然恐亦是方言。而大意则与锢露云云同也。)革初九。本无黄牛之象。只是居初无应。未可有为。初又是刚而不中。所不足者。中顺。故特取黄牛之革。以为此爻之象。不曰有此象而曰为此象者。此也。后凡言为此象。皆仿此。
九三爻辞。谓其过刚不中。躁动于革。故其占为征则必。凶虽征而亦危。然时则当革。故必革言三就。则无过刚躁动之失而人信之矣。此本义之意也。而谚释。以征则凶贞则厉为吐。夫征则凶。过刚之失也。贞则厉。过柔之失也。易中无以贞为厉之例。而若曰一于贞固。而不知变易为厉。则不应于一句内并设此戒也。盖本义之说不详。无以见其有此意。而小注云峰说如此解之。故谚释者。为其所误而然耳。以过刚躁动而征则凶矣。若是者。其事虽正。而亦不免于厉。甚言征之不可矣。
象传又何之矣。程传言稽之公论而已。三就则更何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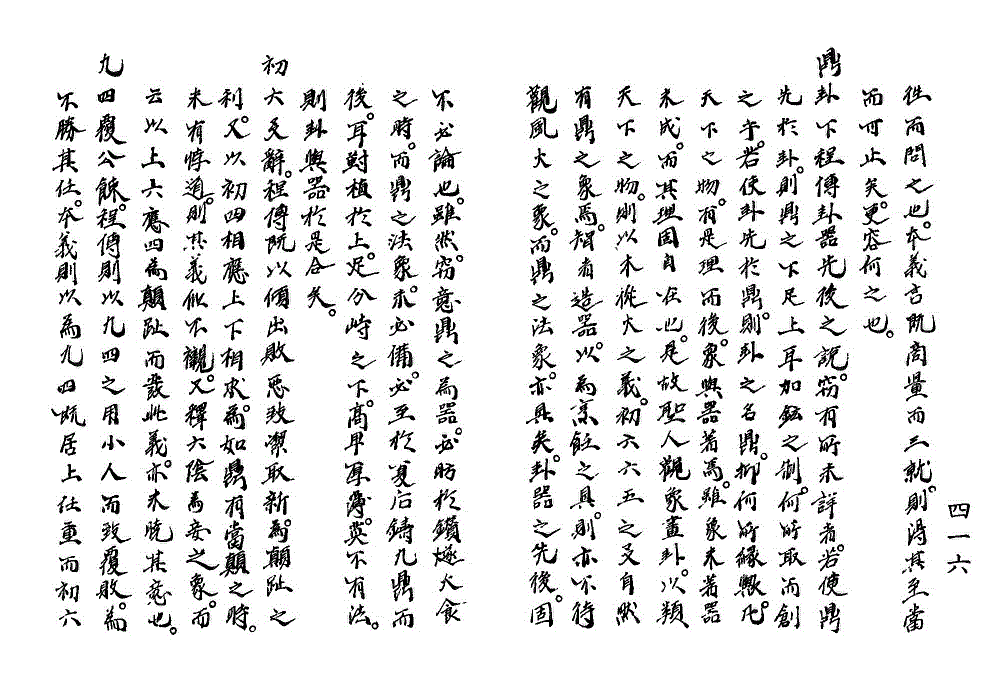 往而问之也。本义言既商量而三就。则得其至当而可止矣。更容何之也。
往而问之也。本义言既商量而三就。则得其至当而可止矣。更容何之也。鼎卦下程传卦器先后之说。窃有所未详者。若使鼎先于卦。则鼎之下足上耳加铉之制。何所取而创之乎。若使卦先于鼎。则卦之名鼎。抑何所缘欤。凡天下之物。有是理而后。象与器著焉。虽象未著器未成。而其理固自在也。是故圣人观象画卦。以类天下之物。则以木从火之义。初六六五之爻自然有鼎之象焉。智者造器。以为烹饪之具。则亦不待观风火之象。而鼎之法象。亦具矣。卦器之先后。固不必论也。虽然。窃意鼎之为器。必昉于钻燧火食之时。而鼎之法象。未必备。必至于夏后铸九鼎而后。耳对植于上。足分峙之下。高卑厚薄。莫不有法。则卦与器于是合矣。
初六爻辞。程传既以倾出败恶致洁取新。为颠趾之利。又以初四相应上下相求。为如鼎有当颠之时。未有悖道。则其义似不衬。又释六阴为妾之象。而云以上六应四为颠趾而发此义。亦未晓其意也。
九四覆公餗。程传则以九四之用小人而致覆败。为不胜其任。本义则以为九四既居上任重而初六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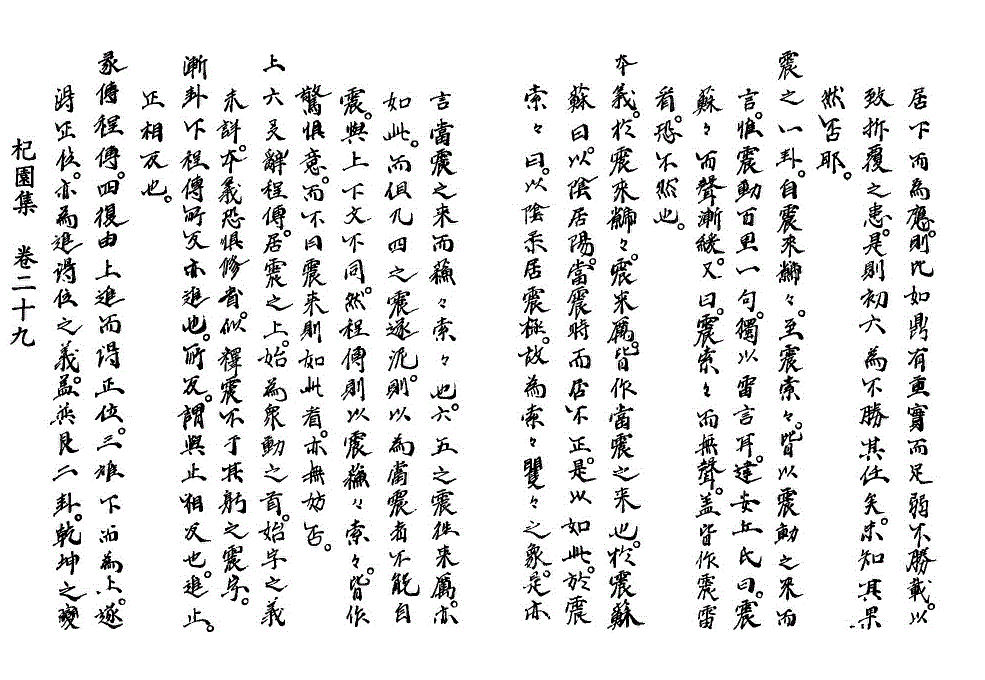 居下而为应。则比如鼎有重实而足弱不胜载。以致拆覆之患。是则初六为不胜其任矣。未知其果然否耶。
居下而为应。则比如鼎有重实而足弱不胜载。以致拆覆之患。是则初六为不胜其任矣。未知其果然否耶。震之一卦。自震来虩虩。至震索索。皆以震动之来而言。惟震动百里一句。独以雷言耳。建安丘氏曰。震苏苏而声渐缓。又曰。震索索而无声。盖皆作震雷看。恐不然也。
本义。于震来虩虩。震来厉。皆作当震之来也。于震苏苏曰。以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以如此。于震索索曰。以阴柔居震极。故为索索矍矍之象。是亦言当震之来而苏苏索索也。六五之震往来厉。亦如此。而但九四之震遂泥。则以为当震者不能自震。与上下文不同。然程传则以震苏苏索索。皆作惊惧意。而不曰震来则如此看。亦无妨否。
上六爻辞程传。居震之上。始为众动之首。始字之义未详。本义恐惧修省。似释震不于其躬之震字。
渐卦下程传所反亦进也。所反。谓与止相反也。进止。正相反也。
彖传程传。四复由上进而得正位。三离下而为上。遂得正位。亦为进得位之义。盖巽艮二卦。乾坤之变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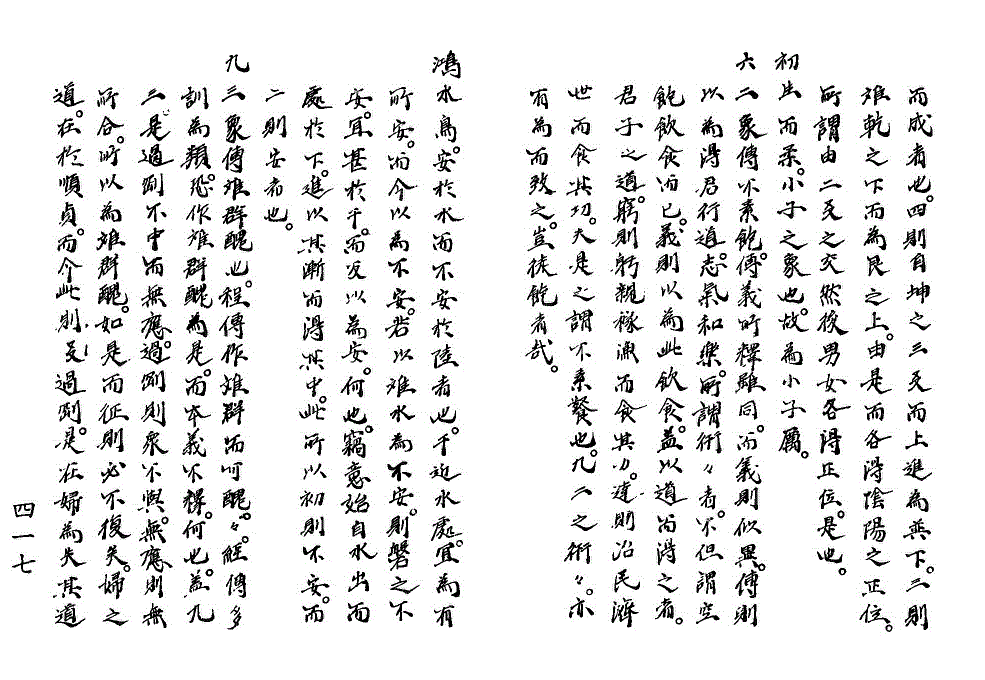 而成者也。四则自坤之三爻而上进为巽下。三则离乾之下而为艮之上。由是而各得阴阳之正位。所谓由二爻之交然后男女各得正位。是也。
而成者也。四则自坤之三爻而上进为巽下。三则离乾之下而为艮之上。由是而各得阴阳之正位。所谓由二爻之交然后男女各得正位。是也。初生而柔。小子之象也。故为小子厉。
六二象传不素饱。传义所释虽同。而义则似异。传则以为得君行道。志气和乐。所谓衎衎者。不但谓空饱饮食而已。义则以为此饮食。盖以道而得之者。君子之道。穷则躬亲稼渔而食其力。达则治民济世而食其功。夫是之谓不素餐也。九二之衎衎。亦有为而致之。岂徒饱者哉。
鸿水鸟。安于水而不安于陆者也。于近水处。宜为有所安。而今以为不安。若以离水为不安。则磐之不安。宜甚于于。而反以为安。何也。窃意始自水出而处于下。进以其渐而得其中。此所以初则不安。而二则安者也。
九三象传离群丑也。程传作离群而可丑。丑。经传多训为类。恐作离群丑为是。而本义不释。何也。盖九三。是过刚不中而无应。过刚则众不与。无应则无所合。所以为离群丑。如是而征则必不复矣。妇之道。在于顺贞。而今此爻则过刚。是在妇为失其道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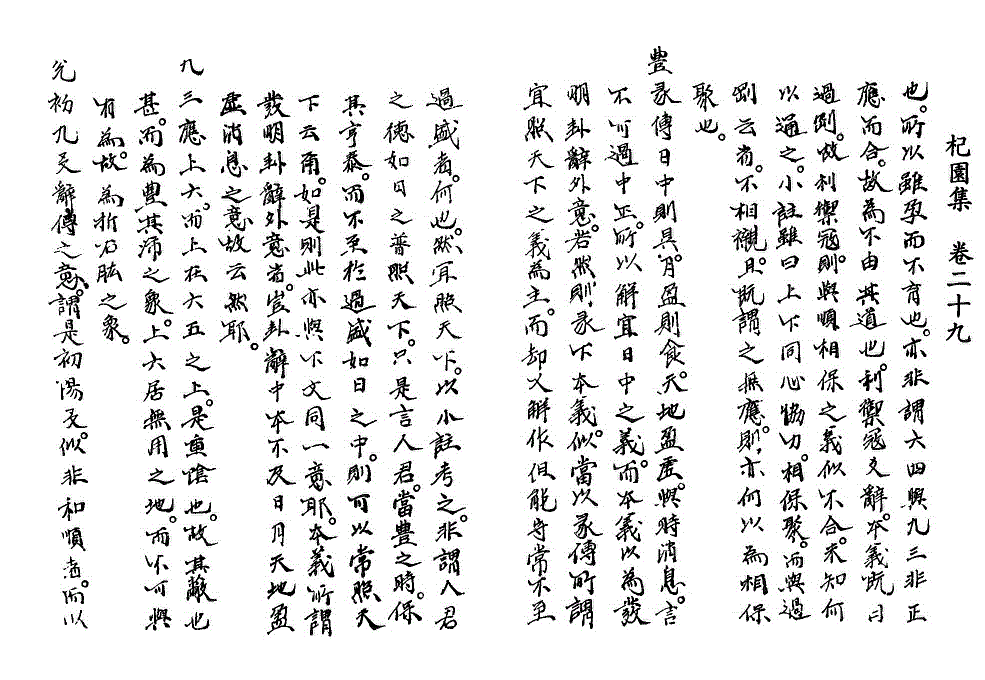 也。所以虽孕而不育也。亦非谓六四与九三非正应而合。故为不由其道也。利御寇爻辞。本义既曰过刚。故利御寇。则与顺相保之义似不合。未知何以通之。小注虽曰上下同心协力。相保聚。而与过刚云者。不相衬。且既谓之无应。则亦何以为相保聚也。
也。所以虽孕而不育也。亦非谓六四与九三非正应而合。故为不由其道也。利御寇爻辞。本义既曰过刚。故利御寇。则与顺相保之义似不合。未知何以通之。小注虽曰上下同心协力。相保聚。而与过刚云者。不相衬。且既谓之无应。则亦何以为相保聚也。礼彖传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言不可过中正。所以解宜日中之义。而本义以为发明卦辞外意。若然则彖下本义。似当以彖传所谓宜照天下之义为主。而却又解作但能守常不至过盛者。何也。然宜照天下。以小注考之。非谓人君之德如日之普照天下。只是言人君。当礼之时。保其亨泰。而不至于过盛如日之中。则可以常照天下云尔。如是则此亦与下文同一意耶。本义所谓发明卦辞外意者。岂卦辞中本不及日月天地盈虚消息之意故云然耶。
九三应上六。而上在六五之上。是重阴也。故其蔽也甚。而为礼其沛之象。上六居无用之地。而不可与有为。故为折右肱之象。
兑初九爻辞传之意。谓是初阳爻。似非和顺者。而以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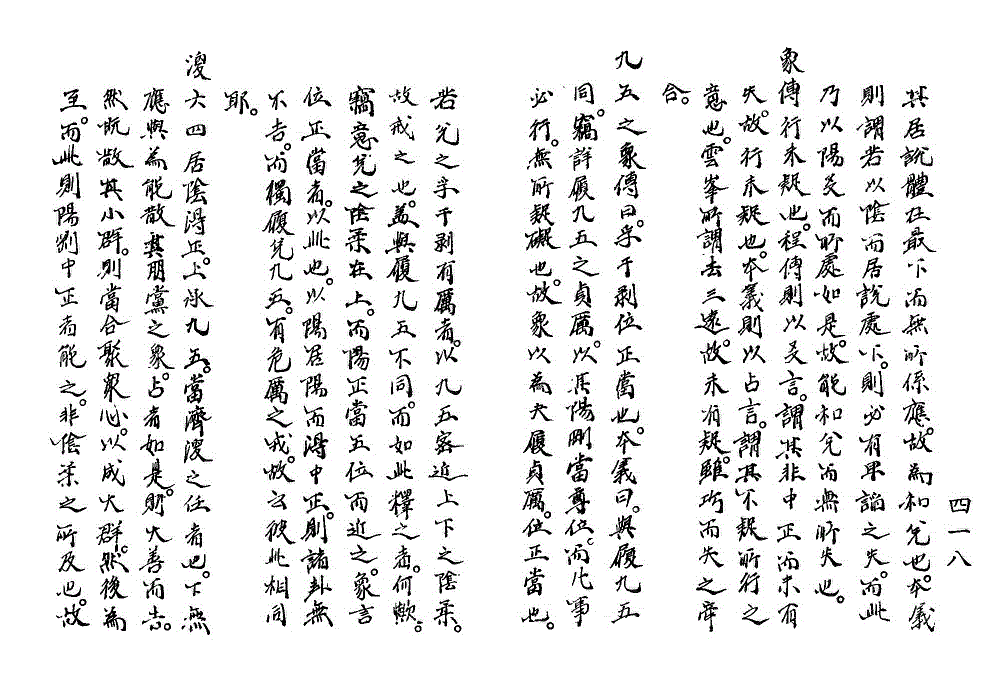 其居说体在最下而无所系应。故为和兑也。本义则谓若以阴而居说处下。则必有卑谄之失。而此乃以阳爻而所处如是。故能和兑而无所失也。
其居说体在最下而无所系应。故为和兑也。本义则谓若以阴而居说处下。则必有卑谄之失。而此乃以阳爻而所处如是。故能和兑而无所失也。象传行未疑也。程传则以爻言。谓其非中正而未有失。故行未疑也。本义则以占言。谓其不疑所行之意也。云峰所谓去三远。故未有疑。虽巧而失之牵合。
九五之象传曰。孚于剥位正当也。本义曰。与履九五同。窃详履九五之贞厉。以其阳刚当尊位。而凡事必行。无所疑碍也。故象以为夫履贞厉。位正当也。若兑之孚于剥有厉者。以九五密近上下之阴柔。故戒之也。盖与履九五不同。而如此释之者。何欤。窃意兑之阴柔在上。而阳正当五位而近之。象言位正当者。以此也。以阳居阳而得中正。则诸卦无不吉。而独履兑九五。有危厉之戒。故云彼此相同耶。
涣六四居阴得正。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者也。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占者如是。则大善而吉。然既散其小群。则当合聚众心。以成大群。然后为至。而此则阳刚中正者能之。非阴柔之所及也。故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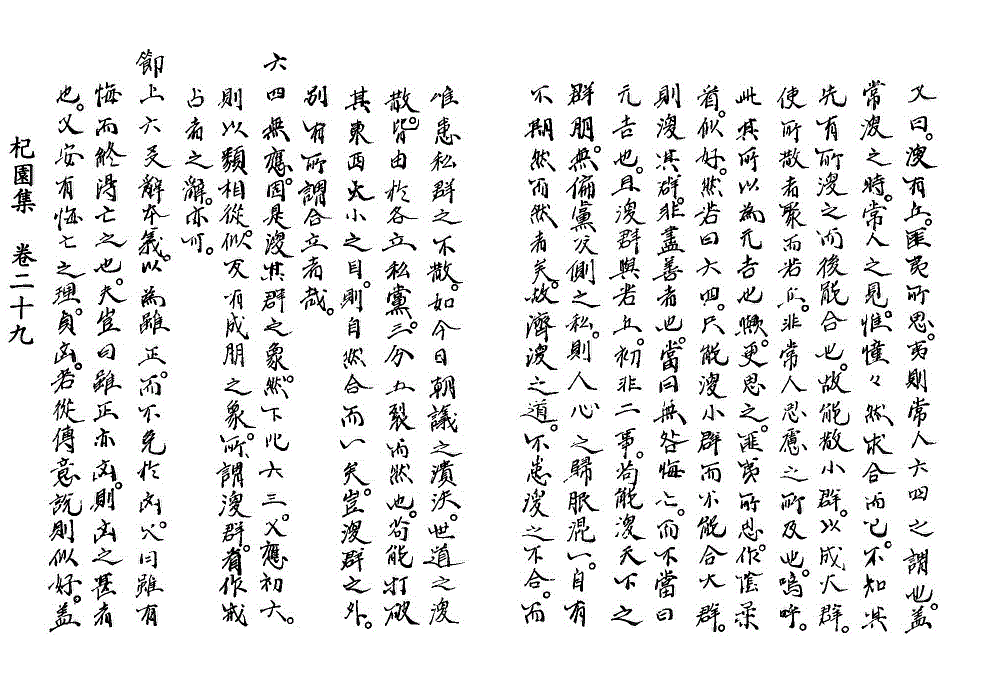 又曰。涣有丘。匪夷所思。夷则常人六四之谓也。盖常涣之时。常人之见。惟憧憧然求合而已。不知其先有所涣之而后能合也。故能散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非常人思虑之所及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元吉也欤。更思之。匪夷所思。作阴柔看。似好。然若曰六四。只能涣小群而不能合大群。则涣其群。非尽善者也。当曰无咎悔亡。而不当曰元吉也。且涣群与若丘。初非二事。苟能涣天下之群朋。无偏党反侧之私。则人心之归服混一。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济涣之道。不患涣之不合。而唯患私群之不散。如今日朝议之溃决。世道之涣散。皆由于各立私党。三分五裂而然也。苟能打破其东西大小之目。则自然合而一矣。岂涣群之外。别有所谓合立者哉。
又曰。涣有丘。匪夷所思。夷则常人六四之谓也。盖常涣之时。常人之见。惟憧憧然求合而已。不知其先有所涣之而后能合也。故能散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非常人思虑之所及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元吉也欤。更思之。匪夷所思。作阴柔看。似好。然若曰六四。只能涣小群而不能合大群。则涣其群。非尽善者也。当曰无咎悔亡。而不当曰元吉也。且涣群与若丘。初非二事。苟能涣天下之群朋。无偏党反侧之私。则人心之归服混一。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济涣之道。不患涣之不合。而唯患私群之不散。如今日朝议之溃决。世道之涣散。皆由于各立私党。三分五裂而然也。苟能打破其东西大小之目。则自然合而一矣。岂涣群之外。别有所谓合立者哉。六四无应。固是涣其群之象。然下比六三。又应初六。则以类相从。似反有成朋之象。所谓涣群。看作戒占者之辞。亦可。
节上六爻辞本义。以为虽正。而不免于凶。又曰虽有悔而终得亡之也。夫岂曰虽正亦凶。则凶之甚者也。又安有悔亡之理。贞凶。若从传意说则似好。盖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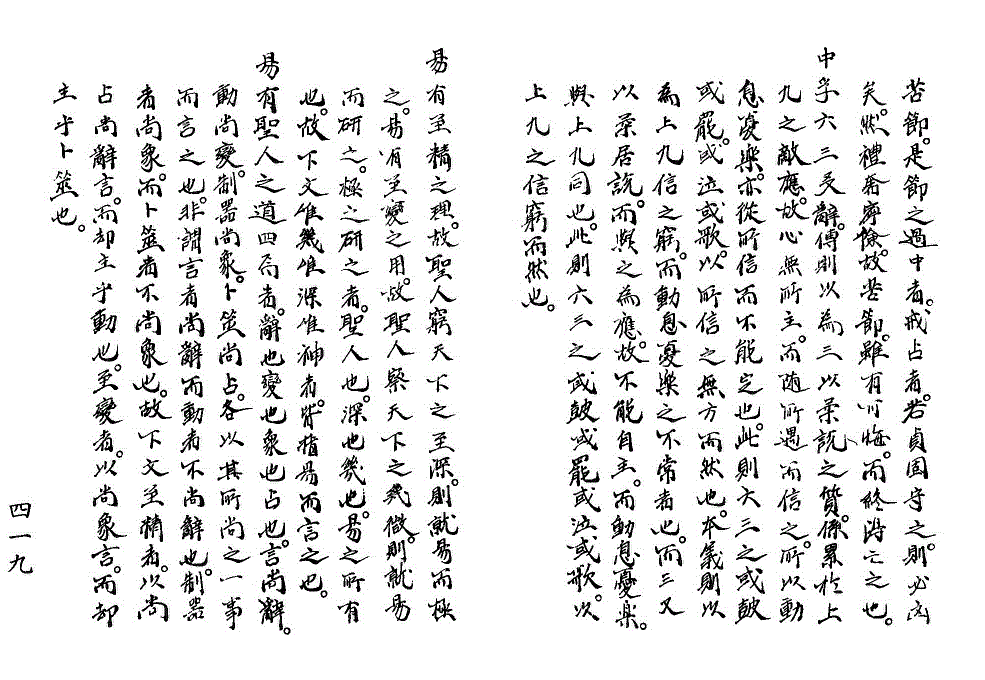 苦节。是节之过中者。戒占者。若贞固守之。则必凶矣。然礼奢宁俭。故苦节。虽有可悔。而终得亡之也。
苦节。是节之过中者。戒占者。若贞固守之。则必凶矣。然礼奢宁俭。故苦节。虽有可悔。而终得亡之也。中孚六三爻辞。传则以为三以柔说之质。系累于上九之敌应。故心无所主。而随所遇而信之。所以动息忧乐。亦从所信而不能定也。此则六三之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以所信之无方而然也。本义则以为上九信之穷。而动息忧乐之不常者也。而三又以柔居说。而与之为应。故不能自主。而动息忧乐。与上九同也。此则六三之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以上九之信穷而然也。
易有至精之理。故圣人穷天下之至深。则就易而极之。易有至变之用。故圣人察天下之几微。则就易而研之。极之研之者。圣人也。深也几也。易之所有也。故下文唯几唯深唯神者。皆指易而言之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辞也变也象也占也。言尚辞。动尚变。制器尚象。卜筮尚占。各以其所尚之一事而言之也。非谓言者尚辞而动者不尚辞也。制器者尚象。而卜筮者不尚象也。故下文至精者。以尚占尚辞言。而却主乎动也。至变者。以尚象言。而却主乎卜筮也。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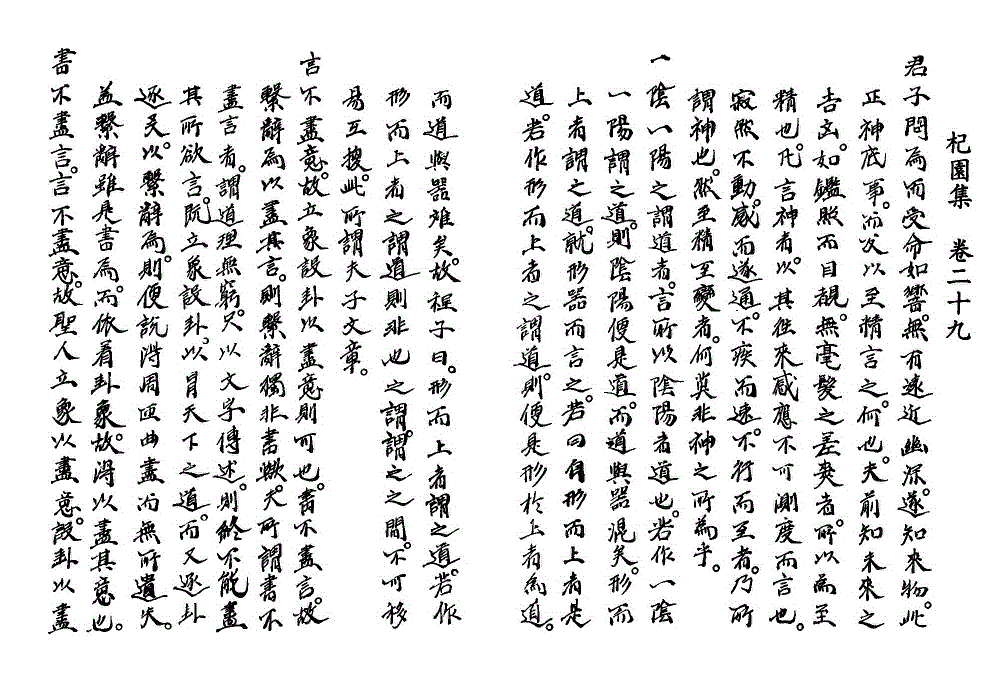 君子问焉而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此正神底事。而反以至精言之。何也。夫前知未来之吉凶。如鉴照而目睹。无毫发之差爽者。所以为至精也。凡言神者。以其往来感应不可测度而言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乃所谓神也。然至精至变者。何莫非神之所为乎。
君子问焉而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此正神底事。而反以至精言之。何也。夫前知未来之吉凶。如鉴照而目睹。无毫发之差爽者。所以为至精也。凡言神者。以其往来感应不可测度而言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乃所谓神也。然至精至变者。何莫非神之所为乎。一阴一阳之谓道者。言所以阴阳者道也。若作一阴一阳谓之道。则阴阳便是道。而道与器混矣。形而上者谓之道。就形器而言之。若曰自形而上者是道。若作形而上者之谓道。则便是形于上者为道。而道与器离矣。故程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若作形而上者之谓道则非也之谓。谓之之间。不可移易互换。此所谓夫子文章。
言不尽意。故立象设卦以尽意则可也。书不尽言。故系辞焉以尽其言。则系辞独非书欤。夫所谓书不尽言者。谓道理无穷。只以文字传述。则终不能尽其所欲言。既立象设卦。以冒天下之道。而又逐卦逐爻。以系辞焉。则便说得周匝曲尽而无所遗失。盖系辞虽是书焉。而依着卦象。故得以尽其意也。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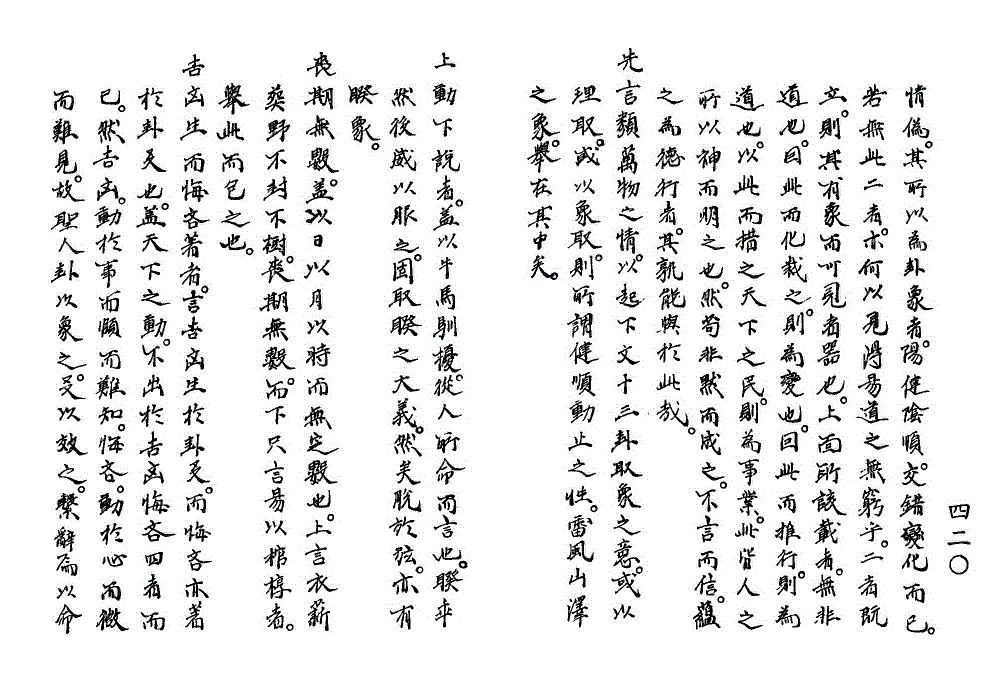 情伪。其所以为卦象者。阳健阴顺。交错变化而已。若无此二者。亦何以见得易道之无穷乎。二者既立。则其有象而可见者器也。上面所该载者。无非道也。因此而化裁之。则为变也。因此而推行。则为道也。以此而措之天下之民。则为事业。此皆人之所以神而明之也。然苟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蕴之为德行者。其孰能与于此哉。
情伪。其所以为卦象者。阳健阴顺。交错变化而已。若无此二者。亦何以见得易道之无穷乎。二者既立。则其有象而可见者器也。上面所该载者。无非道也。因此而化裁之。则为变也。因此而推行。则为道也。以此而措之天下之民。则为事业。此皆人之所以神而明之也。然苟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蕴之为德行者。其孰能与于此哉。先言类万物之情。以起下文十三卦取象之意。或以理取。或以象取。则所谓健顺动止之性。雷风山泽之象。举在其中矣。
上动下说者。盖以牛马驯扰。从人所命而言也。睽乖然后威以服之。固取睽之大义。然矣脱于弦。亦有睽象。
丧期无数。盖以日以月以时而无定数也。上言衣薪葬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而下只言易以棺椁者。举此而包之也。
吉凶生而悔吝著者。言吉凶生于卦爻。而悔吝亦著于卦爻也。盖天下之动。不出于吉凶悔吝四者而已。然吉凶。动于事而颐而难知。悔吝。动于心而微而难见。故圣人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系辞焉以命
杞园集卷之二十九 第 4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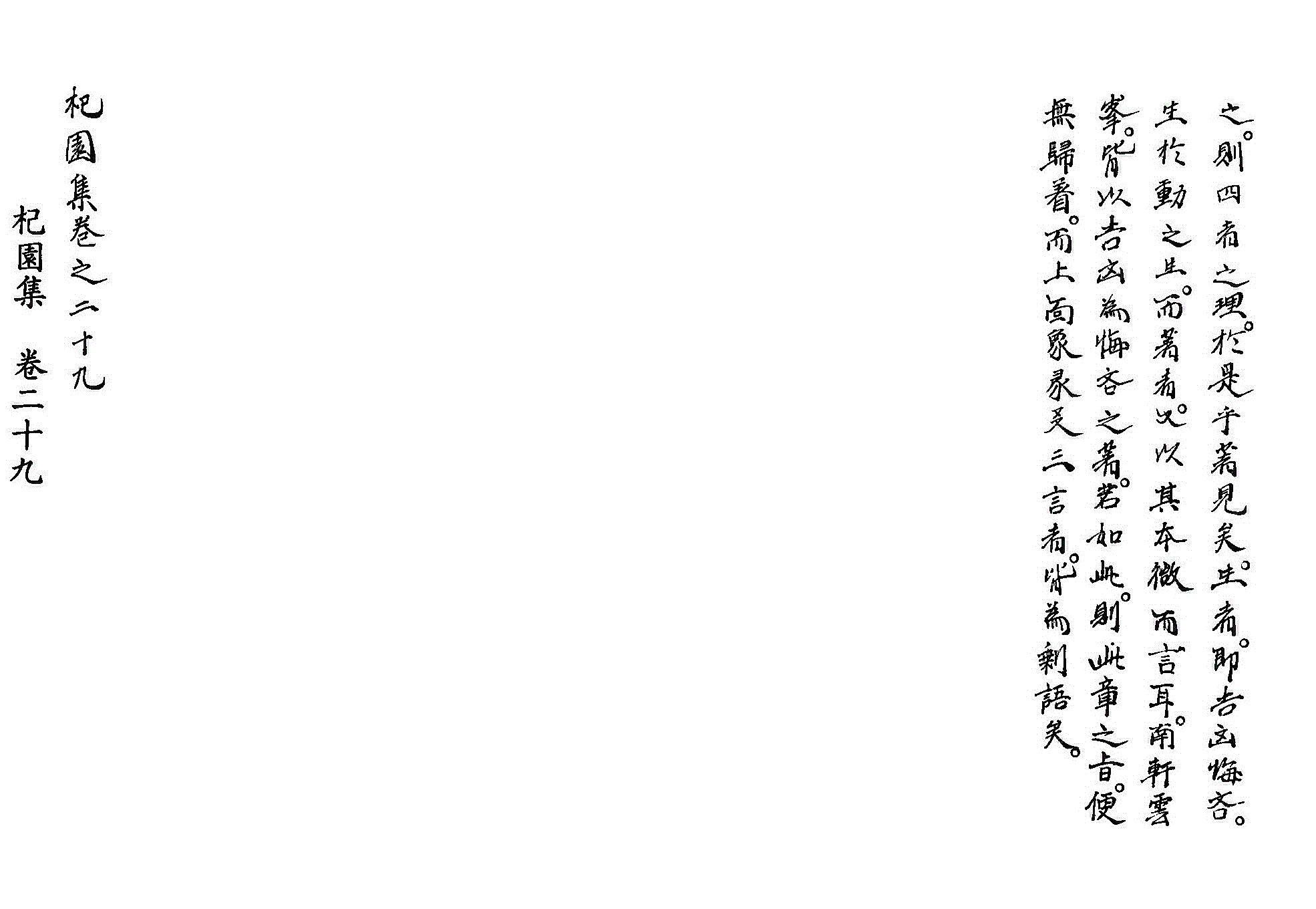 之。则四者之理。于是乎著见矣。生者。即吉凶悔吝。生于动之生。而著者。又以其本微而言耳。南轩云峰。皆以吉凶为悔吝之著。若如此。则此章之旨。便无归着。而上面象彖爻三言者。皆为剩语矣。
之。则四者之理。于是乎著见矣。生者。即吉凶悔吝。生于动之生。而著者。又以其本微而言耳。南轩云峰。皆以吉凶为悔吝之著。若如此。则此章之旨。便无归着。而上面象彖爻三言者。皆为剩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