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x 页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书]
[书]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7H 页
 答尹大源(东洙)书(乙未)
答尹大源(东洙)书(乙未)意外承问。谨审日间启处神相。感慰无以喻弟咳嗽。犹未快瘳。昨又吐血数口。神思索莫。今始似醒然耳。示意谨悉。而第念无论门生与儒林。诚欲举事。必有倡而主之者。苟其倡而主之者。不鄙而见与之谋。则当为之输诚献愚而不辞矣。傥又开示其命意而使之措辞。则亦不敢以辞拙而终辞矣。至于鄙见。元来果以此事为不可少缓。则决不敢靠连多人。假辞他手尔。而今者之事。未知谁为主张。而使弟为谁人搆草耶。钝根固滞。终未知所以承教之方。迁延却顾。以至于今。可叹可闷。第未知吾兄以此等是非。为一时章疏之所可断定者乎。而将来彼此层加。更迭无已。则未知末稍何者为胜而何者为负耶。今者大龄辈之所丑辱。固无复加矣。而言者出于口而无穷者也。吾兄不见怀川碣文时往复及所谓李同甫问答。愈出而愈险。愈往而愈深耶。若此中一疏。正触其忌讳。则彼将鼓翼而起。掇拾馀论。靡有限极。殆张释之所谓设有愚民取长陵一抔土。何以加其罪者也。当此之时。果有能讨其罪而判其是非。如百世后公论之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7L 页
 定者耶。当此之时。为世道之累者当如何。而果能一毫有补于公私耶。幸为之长虑而深思之如何。盖世短而道长。非人为所可促也。柰何柰何。平日此意思。恒在心曲。亦尝开口于一二朋友而无人领可。未敢索言。今则实欲倾倒无馀。而病倦便忙。略举梗概。伏惟恕其戆率而察其衷曲。如何。
定者耶。当此之时。为世道之累者当如何。而果能一毫有补于公私耶。幸为之长虑而深思之如何。盖世短而道长。非人为所可促也。柰何柰何。平日此意思。恒在心曲。亦尝开口于一二朋友而无人领可。未敢索言。今则实欲倾倒无馀。而病倦便忙。略举梗概。伏惟恕其戆率而察其衷曲。如何。拟答尹大源书(乙未)
缕缕诲谕。说尽多少义理。费尽多少说话。奉读再三。不胜感荷。而亦不觉怃然自失。噫。心之相知。固非容易。而言亦不相悉矣。良可慨也。亦可叹也。既蒙勤教。不敢自外。不得不条举来教之一二。以明区区本心之所存。盖龙溪发文。恰过两月。彼中漠然无一人更为提起者。而吾兄忽有此敦迫之教。心所未晓。疏事当否。姑舍勿论。顾吾两人语默之节。实涉无谓。于是有昨日之仰复。而其下一段说义。乃弟之平日本来意见也。此意前此非不提掇。而每如以水扱石。故因此发端。欲其深思。而来教乃如是矣。噫。只此物情之在目前者。犹不肯徐察。尚何望其讲其义理。导其归趣乎。来教曰。今番疏议。出于青洪章甫。则此其为倡而主之者云云。所谓青。即青阳也。洪即洪阳也。青阳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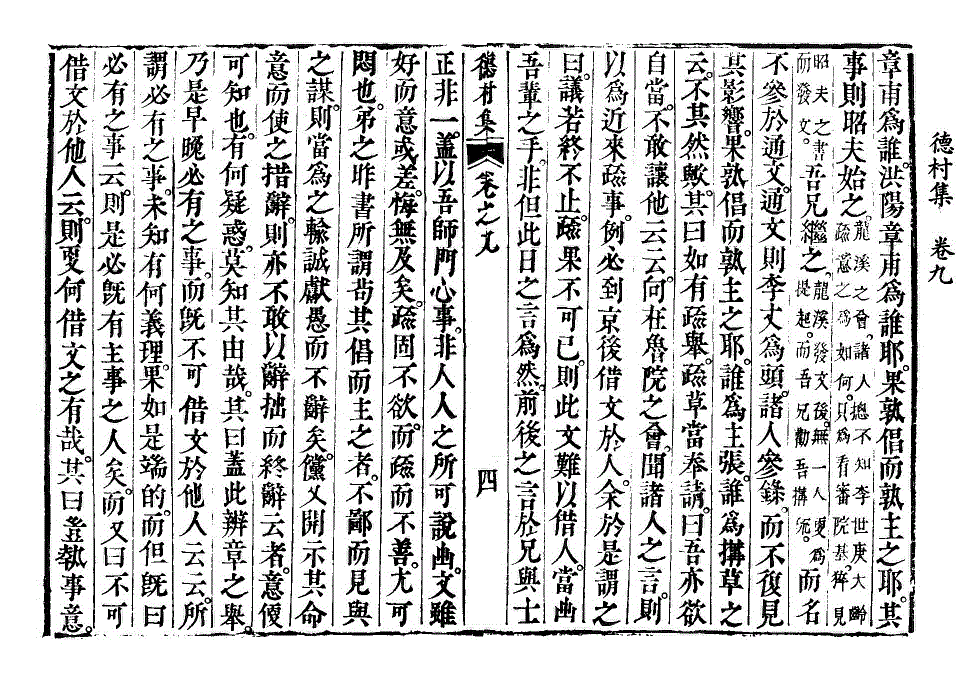 章甫为谁。洪阳章甫为谁耶。果孰倡而孰主之耶。其事则昭夫始之。(龙溪之会。诸人总不知李世庚大龄疏意之为如何。只为看审院基。猝见昭夫之书而发文。)吾兄继之。(龙溪发文后。无一人更为提起。而吾兄劝吾搆疏。)而名不参于通文。通文则李丈为头。诸人参录。而不复见其影响。果孰倡而孰主之耶。谁为主张。谁为搆草之云。不其然欤。其曰如有疏举。疏草当奉请。曰吾亦欲自当。不敢让他云云。向在鲁院之会。闻诸人之言。则以为近来疏事。例必到京后借文于人。余于是谓之曰。议若终不止。疏果不可已。则此文难以借人。当出吾辈之手。非但此日之言为然。前后之言于兄与士正非一。盖以吾师门心事。非人人之所可说出。文虽好而意或差。悔无及矣。疏固不欲。而疏而不善。尤可闷也。弟之昨书所谓苟其倡而主之者。不鄙而见与之谋。则当为之输诚献愚而不辞矣。傥又开示其命意而使之措辞。则亦不敢以辞拙而终辞云者。意便可知也。有何疑惑。莫知其由哉。其曰盖此辨章之举。乃是早晚必有之事。而既不可借文于他人云云。所谓必有之事。未知有何义理。果如是端的。而但既曰必有之事云。则是必既有主事之人矣。而又曰不可借文于他人云。则更何借文之有哉。其曰岂执事意。
章甫为谁。洪阳章甫为谁耶。果孰倡而孰主之耶。其事则昭夫始之。(龙溪之会。诸人总不知李世庚大龄疏意之为如何。只为看审院基。猝见昭夫之书而发文。)吾兄继之。(龙溪发文后。无一人更为提起。而吾兄劝吾搆疏。)而名不参于通文。通文则李丈为头。诸人参录。而不复见其影响。果孰倡而孰主之耶。谁为主张。谁为搆草之云。不其然欤。其曰如有疏举。疏草当奉请。曰吾亦欲自当。不敢让他云云。向在鲁院之会。闻诸人之言。则以为近来疏事。例必到京后借文于人。余于是谓之曰。议若终不止。疏果不可已。则此文难以借人。当出吾辈之手。非但此日之言为然。前后之言于兄与士正非一。盖以吾师门心事。非人人之所可说出。文虽好而意或差。悔无及矣。疏固不欲。而疏而不善。尤可闷也。弟之昨书所谓苟其倡而主之者。不鄙而见与之谋。则当为之输诚献愚而不辞矣。傥又开示其命意而使之措辞。则亦不敢以辞拙而终辞云者。意便可知也。有何疑惑。莫知其由哉。其曰盖此辨章之举。乃是早晚必有之事。而既不可借文于他人云云。所谓必有之事。未知有何义理。果如是端的。而但既曰必有之事云。则是必既有主事之人矣。而又曰不可借文于他人云。则更何借文之有哉。其曰岂执事意。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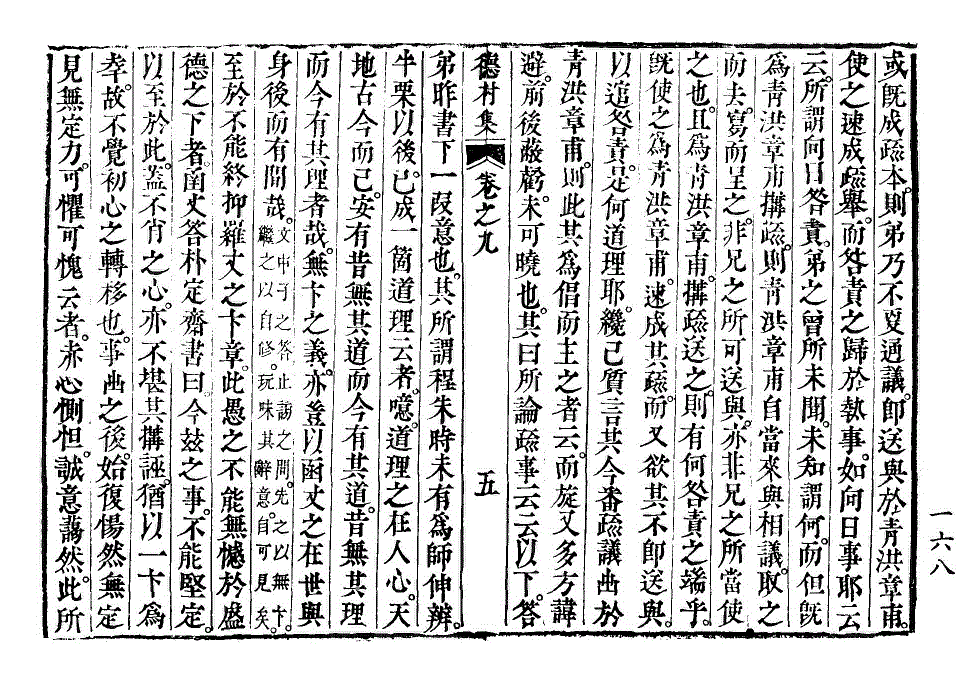 或既成疏本。则弟乃不更通议。即送与于青洪章甫。使之速成疏举。而咎责之归于执事。如向日事耶云云。所谓向日咎责。弟之曾所未闻。未知谓何。而但既为青洪章甫搆疏。则青洪章甫自当来与相议。取之而去。写而呈之。非兄之所可送与。亦非兄之所当使之也。且为青洪章甫。搆疏送之。则有何咎责之端乎。既使之为青洪章甫。速成其疏。而又欲其不即送与。以逭咎责。是何道理耶。才已质言其今番疏议出于青洪章甫。则此其为倡而主之者云。而旋又多方讳避。前后蔽亏。未可晓也。其曰所论疏事云云以下。答弟昨书下一段意也。其所谓程朱时未有为师伸辨。牛栗以后。已成一个道理云者。噫。道理之在人心。天地古今而已。安有昔无其道而今有其道。昔无其理而今有其理者哉。无卞之义。亦岂以函丈之在世与身后而有间哉。(文中子之答止谤之问。先之以无卞。继之以自修。玩味其辞意。自可见矣。)至于不能终抑罗丈之卞章。此愚之不能无憾于盛德之下者。函丈答朴定斋书曰。今玆之事。不能坚定。以至于此。盖不肖之心。亦不堪其搆诬。犹以一卞为幸。故不觉初心之转移也。事出之后。始复惕然无定见无定力。可惧可愧云者。赤心恻怛。诚意蔼然。此所
或既成疏本。则弟乃不更通议。即送与于青洪章甫。使之速成疏举。而咎责之归于执事。如向日事耶云云。所谓向日咎责。弟之曾所未闻。未知谓何。而但既为青洪章甫搆疏。则青洪章甫自当来与相议。取之而去。写而呈之。非兄之所可送与。亦非兄之所当使之也。且为青洪章甫。搆疏送之。则有何咎责之端乎。既使之为青洪章甫。速成其疏。而又欲其不即送与。以逭咎责。是何道理耶。才已质言其今番疏议出于青洪章甫。则此其为倡而主之者云。而旋又多方讳避。前后蔽亏。未可晓也。其曰所论疏事云云以下。答弟昨书下一段意也。其所谓程朱时未有为师伸辨。牛栗以后。已成一个道理云者。噫。道理之在人心。天地古今而已。安有昔无其道而今有其道。昔无其理而今有其理者哉。无卞之义。亦岂以函丈之在世与身后而有间哉。(文中子之答止谤之问。先之以无卞。继之以自修。玩味其辞意。自可见矣。)至于不能终抑罗丈之卞章。此愚之不能无憾于盛德之下者。函丈答朴定斋书曰。今玆之事。不能坚定。以至于此。盖不肖之心。亦不堪其搆诬。犹以一卞为幸。故不觉初心之转移也。事出之后。始复惕然无定见无定力。可惧可愧云者。赤心恻怛。诚意蔼然。此所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9H 页
 以为吾函丈盛德也。恐不可以一时撝谦之言而看也。且丁卯一疏。定百世公案云。则何至今纷纷不已耶。若夫士论之不可沮则诚然矣。而以弟之不制其疏。谓之沮士论则大不然。既谓之士论。则人谁为之劝沮。亦岂被人劝沮。有所前却耶。且焉有因人之不制其疏。而遂以自沮之士论也。罗丈之于老先生。不可以士论言。而当时罗丈励志锐气。制疏以待。累被函丈譬晓。而终不回挠。非函丈之挽之不力也。以罗丈意见。不被沮于函丈之挽之也。今日青洪章甫苟有一人如罗丈之励志锐气。则犹可以劝沮言也。今已数月。汔未闻其谁为主张。谁更提起。则尚何有可以劝可以沮者乎。彼则漠然。而吾兄每劝吾制疏。弟亦曰苟其倡而主之者与之谋。则当为之输诚。是则殆近于鼓之动之。谓之劝之。亦太歇后。沮之一字。著不可得矣。无益于事。有慊于义。吾两人语默。实涉无谓矣。所谓彼则无所不至。此则噤无一语。彼则气豪意健。此则畏首畏尾云云。是则惟以血战求胜为务。正兵家所谓譬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也。此非迂儒所敢闻也。况此方求胜。彼亦求胜。一向如此不已。毕竟何所底止耶。弟之昨书所谓未知末梢何者
以为吾函丈盛德也。恐不可以一时撝谦之言而看也。且丁卯一疏。定百世公案云。则何至今纷纷不已耶。若夫士论之不可沮则诚然矣。而以弟之不制其疏。谓之沮士论则大不然。既谓之士论。则人谁为之劝沮。亦岂被人劝沮。有所前却耶。且焉有因人之不制其疏。而遂以自沮之士论也。罗丈之于老先生。不可以士论言。而当时罗丈励志锐气。制疏以待。累被函丈譬晓。而终不回挠。非函丈之挽之不力也。以罗丈意见。不被沮于函丈之挽之也。今日青洪章甫苟有一人如罗丈之励志锐气。则犹可以劝沮言也。今已数月。汔未闻其谁为主张。谁更提起。则尚何有可以劝可以沮者乎。彼则漠然。而吾兄每劝吾制疏。弟亦曰苟其倡而主之者与之谋。则当为之输诚。是则殆近于鼓之动之。谓之劝之。亦太歇后。沮之一字。著不可得矣。无益于事。有慊于义。吾两人语默。实涉无谓矣。所谓彼则无所不至。此则噤无一语。彼则气豪意健。此则畏首畏尾云云。是则惟以血战求胜为务。正兵家所谓譬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也。此非迂儒所敢闻也。况此方求胜。彼亦求胜。一向如此不已。毕竟何所底止耶。弟之昨书所谓未知末梢何者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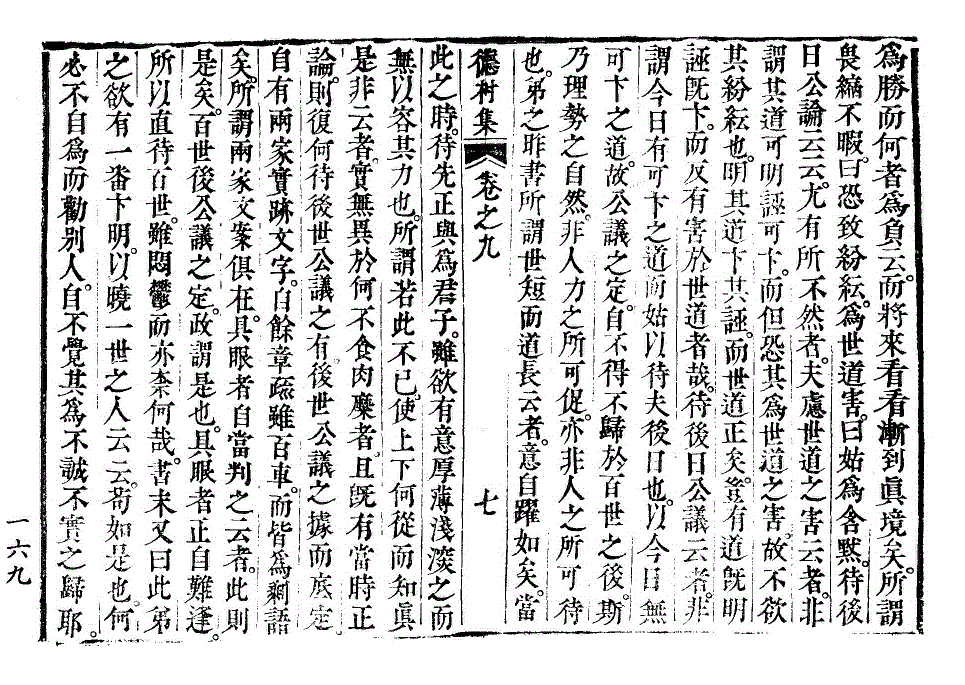 为胜而何者为负云。而将来看看渐到真境矣。所谓畏缩不暇。曰恐致纷纭。为世道害。曰姑为含默。待后日公论云云。尤有所不然者。夫虑世道之害云者。非谓其道可明诬可卞。而但恐其为世道之害。故不欲其纷纭也。明其道卞其诬。而世道正矣。岂有道既明诬既卞。而反有害于世道者哉。待后日公议云者。非谓今日有可卞之道而姑以待夫后日也。以今日无可卞之道。故公议之定。自不得不归于百世之后。斯乃理势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可促。亦非人之所可待也。弟之昨书所谓世短而道长云者。意自跃如矣。当此之时。待先正与为君子。虽欲有意厚薄浅深之而无以容其力也。所谓若此不已。使上下何从而知真是非云者。实无异于何不食肉糜者。且既有当时正论。则复何待后世公议之有。后世公议之据而底定。自有两家实迹文字。自馀章疏虽百车。而皆为剩语矣。所谓两家文案俱在。具眼者自当判之云者。此则是矣。百世后公议之定。政谓是也。具眼者正自难逢。所以直待百世。虽闷郁而亦柰何哉。书末又曰此弟之欲有一番卞明。以晓一世之人云云。苟如是也。何必不自为而劝别人。自不觉其为不诚不实之归耶。
为胜而何者为负云。而将来看看渐到真境矣。所谓畏缩不暇。曰恐致纷纭。为世道害。曰姑为含默。待后日公论云云。尤有所不然者。夫虑世道之害云者。非谓其道可明诬可卞。而但恐其为世道之害。故不欲其纷纭也。明其道卞其诬。而世道正矣。岂有道既明诬既卞。而反有害于世道者哉。待后日公议云者。非谓今日有可卞之道而姑以待夫后日也。以今日无可卞之道。故公议之定。自不得不归于百世之后。斯乃理势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可促。亦非人之所可待也。弟之昨书所谓世短而道长云者。意自跃如矣。当此之时。待先正与为君子。虽欲有意厚薄浅深之而无以容其力也。所谓若此不已。使上下何从而知真是非云者。实无异于何不食肉糜者。且既有当时正论。则复何待后世公议之有。后世公议之据而底定。自有两家实迹文字。自馀章疏虽百车。而皆为剩语矣。所谓两家文案俱在。具眼者自当判之云者。此则是矣。百世后公议之定。政谓是也。具眼者正自难逢。所以直待百世。虽闷郁而亦柰何哉。书末又曰此弟之欲有一番卞明。以晓一世之人云云。苟如是也。何必不自为而劝别人。自不觉其为不诚不实之归耶。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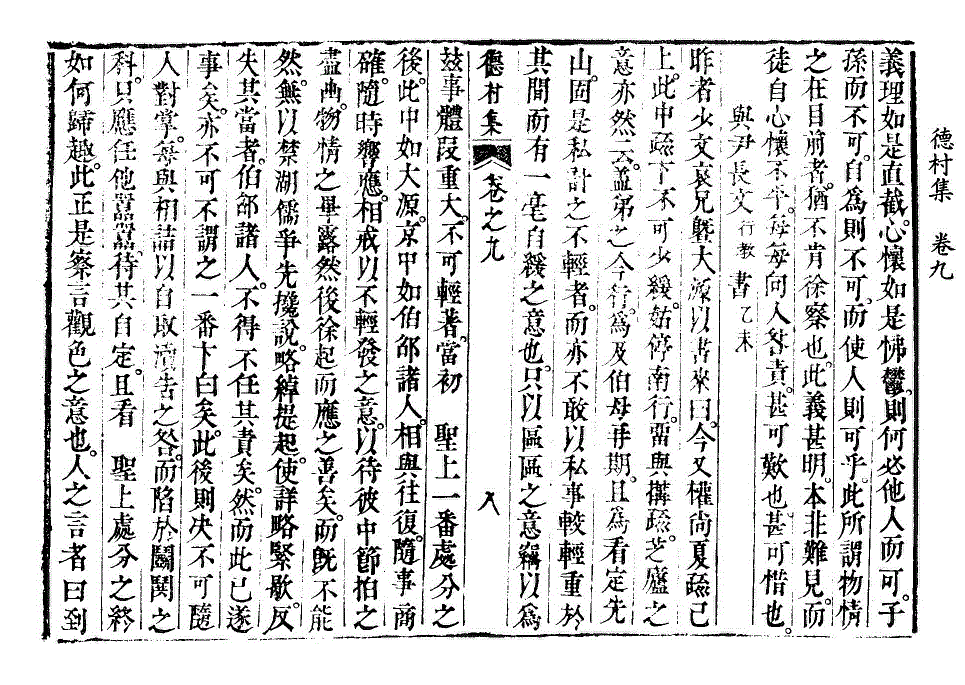 义理如是直截。心怀如是怫郁。则何必他人而可。子孙而不可。自为则不可。而使人则可乎。此所谓物情之在目前者。犹不肯徐察也。此义甚明。本非难见。而徒自心怀不平。每每向人咎责。甚可叹也。甚可惜也。
义理如是直截。心怀如是怫郁。则何必他人而可。子孙而不可。自为则不可。而使人则可乎。此所谓物情之在目前者。犹不肯徐察也。此义甚明。本非难见。而徒自心怀不平。每每向人咎责。甚可叹也。甚可惜也。与尹长文(行教)书(乙未)
昨者少文哀兄暨大源以书来曰。今又权尚夏疏已上。此中疏卞不可少缓。姑停南行。留与搆疏。芝庐之意亦然云。盖弟之今行。为及伯母再期。且为看定先山。固是私计之不轻者。而亦不敢以私事较轻重于其间而有一毫自缓之意也。只以区区之意窃以为玆事体段重大。不可轻著。当初 圣上一番处分之后。此中如大源。京中如伯邵诸人。相与往复。随事商确。随时响应。相戒以不轻发之意。以待彼中节拍之尽出。物情之毕露然后徐起而应之善矣。而既不能然。无以禁湖儒争先搀说。略绰提起。使详略紧歇。反失其当者。伯邵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矣。然而此已遂事矣。亦不可不谓之一番卞白矣。此后则决不可随人对掌。每与相诘以自取渎告之咎。而陷于斗鬨之科。只应任他嚣嚣。待其自定。且看 圣上处分之终如何归趣。此正是察言观色之意也。人之言者曰到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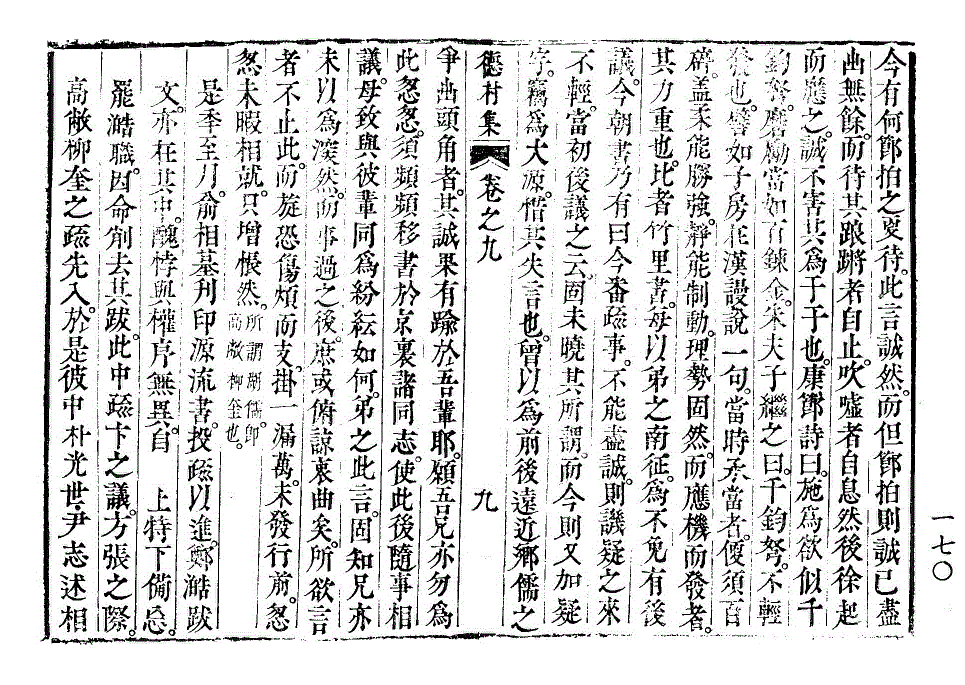 今有何节拍之更待。此言诚然。而但节拍则诚已尽出无馀。而待其踉蹡者自止。吹嘘者自息然后徐起而应之。诚不害其为于于也。康节诗曰。施为欲似千钧弩。磨励当如百鍊金。朱夫子继之曰。千钧弩。不轻发也。譬如子房在汉谩说一句。当时承当者。便须百碎。盖柔能胜强。静能制动。理势固然。而应机而发者。其力重也。比者竹里书。每以弟之南征。为不免有后议。今朝书乃有曰今番疏事。不能尽诚。则讥疑之来不轻。当初后议之云。固未晓其所谓。而今则又加疑字。窃为大源。惜其失言也。曾以为前后远近乡儒之争出头角者。其诚果有踰于吾辈耶。愿吾兄亦勿为此匆匆。须频频移书于京里诸同志。使此后随事相议。毋致与彼辈同为纷纭如何。弟之此言。固知兄亦未以为深然。而事过之后。庶或俯谅衷曲矣。所欲言者不止此。而旋恐伤烦而支。挂一漏万。未发行前。匆匆未暇相就。只增怅然。(所谓湖儒。即高敝柳奎也。)
今有何节拍之更待。此言诚然。而但节拍则诚已尽出无馀。而待其踉蹡者自止。吹嘘者自息然后徐起而应之。诚不害其为于于也。康节诗曰。施为欲似千钧弩。磨励当如百鍊金。朱夫子继之曰。千钧弩。不轻发也。譬如子房在汉谩说一句。当时承当者。便须百碎。盖柔能胜强。静能制动。理势固然。而应机而发者。其力重也。比者竹里书。每以弟之南征。为不免有后议。今朝书乃有曰今番疏事。不能尽诚。则讥疑之来不轻。当初后议之云。固未晓其所谓。而今则又加疑字。窃为大源。惜其失言也。曾以为前后远近乡儒之争出头角者。其诚果有踰于吾辈耶。愿吾兄亦勿为此匆匆。须频频移书于京里诸同志。使此后随事相议。毋致与彼辈同为纷纭如何。弟之此言。固知兄亦未以为深然。而事过之后。庶或俯谅衷曲矣。所欲言者不止此。而旋恐伤烦而支。挂一漏万。未发行前。匆匆未暇相就。只增怅然。(所谓湖儒。即高敝柳奎也。)是年至月。俞相基刊印源流书。投疏以进。郑浩跋文。亦在其中。丑悖与权序无异。自 上特下备忘。罢浩职。因命削去其跋。此中疏卞之议。方张之际。高敝柳奎之疏先入。于是彼中朴光世,尹志述相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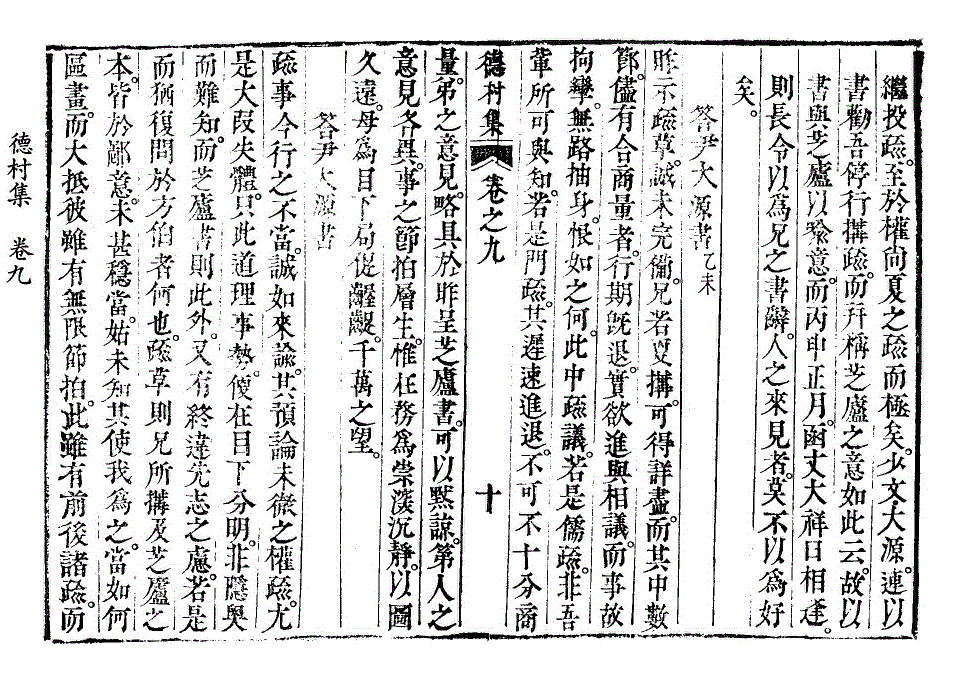 继投疏。至于权尚夏之疏而极矣。少文,大源。连以书劝吾停行搆疏。而并称芝庐之意如此云。故以书与芝庐以喻意。而丙申正月。函丈大祥日相逢。则长令以为兄之书辞。人之来见者。莫不以为好矣。
继投疏。至于权尚夏之疏而极矣。少文,大源。连以书劝吾停行搆疏。而并称芝庐之意如此云。故以书与芝庐以喻意。而丙申正月。函丈大祥日相逢。则长令以为兄之书辞。人之来见者。莫不以为好矣。答尹大源书(乙未)
昨示疏草。诚未完备。兄若更搆。可得详尽。而其中数节。尽有合商量者。行期既退。实欲进与相议。而事故拘挛。无路抽身。恨如之何。此中疏议。若是儒疏。非吾辈所可与知。若是门疏。其迟速进退。不可不十分商量。弟之意见。略具于昨呈芝庐书。可以默谅。第人之意见各异。事之节拍层生。惟在务为崇深沉静。以图久远。毋为目下局促龌龊。千万之望。
答尹大源书
疏事今行之不当。诚如来谕。其预论未彻之权疏。尤是大段失体。只此道理事势。便在目下分明。非隐奥而难知。而芝庐书则此外。又有终违先志之虑。若是而犹复问于方伯者何也。疏草则兄所搆及芝庐之本。皆于鄙意。未甚稳当。姑未知其使我为之。当如何区画。而大抵彼虽有无限节拍。此虽有前后诸疏。而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1L 页
 只是为源流一事。既为一事而卞明。则虽使前后累疏。疏各异手。不可不立定大意以为主干。而其枝叶之随节拍而有详略者。亦不可不前后照管。如出一手。元来此事。自有正大道理明白事證。如青天白日。此正是大意主干。虽至于十疏而不可易者也。至于俞之初以为小注始有两祖之笔。而后又以为假使吕东莱尽写四书章句。独不为朱子书乎云云。及权之到今。创为市南在林川。编集解之说。如此之类。直是遁辞之知所穷。小人之无忌惮也。只令明示大义而责其诬罔。因喝其不能供證。邦有常刑而已。决不可自我憧憧。费力分疏。指定其集解之为某说也。弟之顷搆疏草。乃是源流。进 御之初。诸疏未上之时。最初发头者。故先举道理事證之大致。要以为向后主干之大指者也。芝庐之以为条卞未备者。只为坐在目今节拍尽出后看故也。然历观诸人之见。类多拖引枝叶上去。沈没琐细中。入于大意主干。渐以歇后。(窃见诸疏本。则为芝庐发明甚力。几乎不见源流本来事实。)宜乎以弟之所作。为条卞未备也。兄之呈芝庐书大义尽好。而其中说及弟处。于私议极未安。弟之本意。实欲避临事主张之嫌。而及被李奎庆甫一言之后。尤不敢轻易开口。
只是为源流一事。既为一事而卞明。则虽使前后累疏。疏各异手。不可不立定大意以为主干。而其枝叶之随节拍而有详略者。亦不可不前后照管。如出一手。元来此事。自有正大道理明白事證。如青天白日。此正是大意主干。虽至于十疏而不可易者也。至于俞之初以为小注始有两祖之笔。而后又以为假使吕东莱尽写四书章句。独不为朱子书乎云云。及权之到今。创为市南在林川。编集解之说。如此之类。直是遁辞之知所穷。小人之无忌惮也。只令明示大义而责其诬罔。因喝其不能供證。邦有常刑而已。决不可自我憧憧。费力分疏。指定其集解之为某说也。弟之顷搆疏草。乃是源流。进 御之初。诸疏未上之时。最初发头者。故先举道理事證之大致。要以为向后主干之大指者也。芝庐之以为条卞未备者。只为坐在目今节拍尽出后看故也。然历观诸人之见。类多拖引枝叶上去。沈没琐细中。入于大意主干。渐以歇后。(窃见诸疏本。则为芝庐发明甚力。几乎不见源流本来事实。)宜乎以弟之所作。为条卞未备也。兄之呈芝庐书大义尽好。而其中说及弟处。于私议极未安。弟之本意。实欲避临事主张之嫌。而及被李奎庆甫一言之后。尤不敢轻易开口。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2H 页
 须千万俯谅。此后勿以此等说说及于他人也。此在弟非小可事尔。芝庐书还呈耳。
须千万俯谅。此后勿以此等说说及于他人也。此在弟非小可事尔。芝庐书还呈耳。答尹长文(丙申)
示意谨悉。而但未知 上之俯索此文字者。有何事端而然耶。别无事端而特命誊进。则只当恭依誊进。以俟更有 下问或处分然后随宜进说而已。若或因某人进说而有是 命。则承是 命而进是说。必有其人。此在义理事体。自有不得不然与不可不尔之门路。惟当平心随事而应之而已。正不须过虑而预为之憧憧也。所谓急伻。谁人遣来。欲兄进呈前后往复书者。事体果有不得不尔之势。而不涉于无端否。假使必进呈往复书然后方是恔于吾心。此两件文字誊进之后。似必自然拖到可以进呈往复书之境。姑须安意以待之如何。目下事。必有方任其责者矣。即当进去。
右丙申七月之初。因权世恒疏。自 上使之誊进怀川所撰鲁西墓碣文及函丈辛酉年拟与怀川书。此时适以吴遂元,李献章诸人科事。 上心方激恼于少辈。而权疏投间而入。少辈之㥘方深。尹拙以朝廷诸人之意。急走人来报于长令。使之进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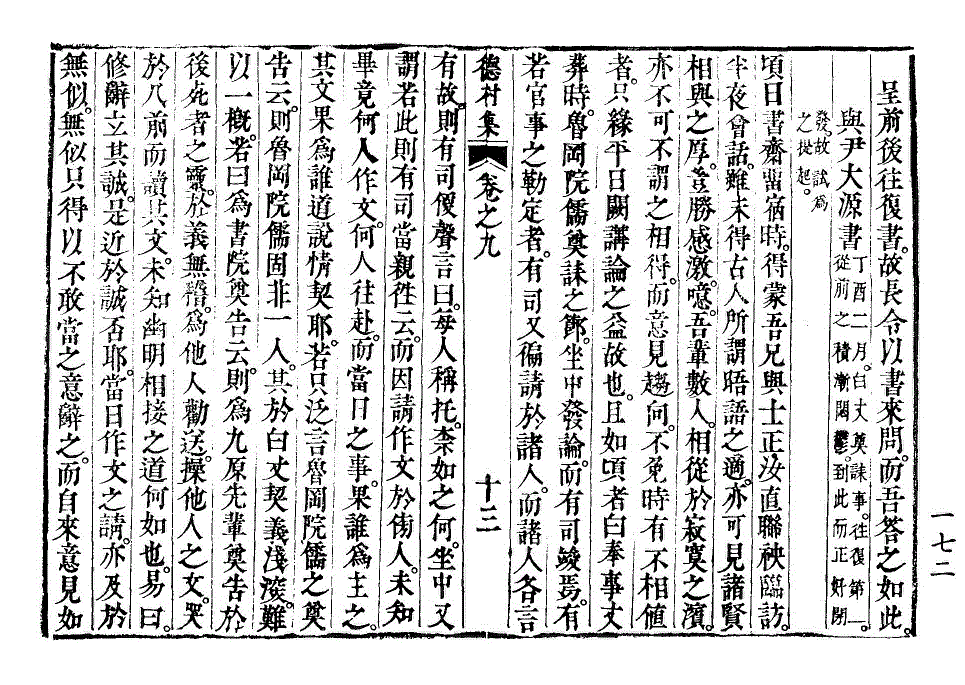 呈前后往复书。故长令以书来问。而吾答之如此。
呈前后往复书。故长令以书来问。而吾答之如此。与尹大源书(丁酉二月。白丈奠诔事。往复第一。从前之积渐闷郁。到此而正好开发。故试为之提起。)
顷日书斋留宿时。得蒙吾兄与士正,汝直联䄃(一作袂)临访。半夜会话。虽未得古人所谓晤语之适。亦可见诸贤相与之厚。岂胜感激。噫。吾辈数人。相从于寂寞之滨。亦不可不谓之相得。而意见趋向。不免时有不相值者。只缘平日阙讲论之益故也。且如顷者白奉事丈葬时。鲁冈院儒奠诔之节。坐中发论。而有司竣焉。有若官事之勒定者。有司又遍请于诸人。而诸人各言有故。则有司便声言曰。每人称托。柰如之何。坐中又谓若此则有司当亲往云。而因请作文于傍人。未知毕竟何人作文。何人往赴。而当日之事。果谁为主之。其文果为谁道说情契耶。若只泛言鲁冈院儒之奠告云。则鲁冈院儒固非一人。其于白丈契义浅深。难以一概。若曰为书院奠告云。则为九原先辈奠告于后死者之灵。于义无稽。为他人劝送。操他人之文。哭于几前而读其文。未知幽明相接之道何如也。易曰。修辞立其诚。是近于诚否耶。当日作文之请。亦及于无似。无似只得以不敢当之意辞之。而自来意见如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3H 页
 此。不觉到处逢源。非有意而为之也。然而区区力量。本不出自家躯壳一分之外。若非左右劝有司往。承宣令兄。劝吾作文。则惟当目睹之心知之而已。又何必为吾兄开喙耶。兄试思此一义。浅虑所及。果为无端否。苟于此一义。不至大相牴牾。则平日之枘凿。庶将渐有同归之望矣。无似之欲得讲磨之资于诸贤久矣。承宣令兄曩以一书叩之而不见其答。士正,汝直则又全不相悉。诚没柰何。若蒙吾兄特谅愚衷。终遂教之则幸矣。
此。不觉到处逢源。非有意而为之也。然而区区力量。本不出自家躯壳一分之外。若非左右劝有司往。承宣令兄。劝吾作文。则惟当目睹之心知之而已。又何必为吾兄开喙耶。兄试思此一义。浅虑所及。果为无端否。苟于此一义。不至大相牴牾。则平日之枘凿。庶将渐有同归之望矣。无似之欲得讲磨之资于诸贤久矣。承宣令兄曩以一书叩之而不见其答。士正,汝直则又全不相悉。诚没柰何。若蒙吾兄特谅愚衷。终遂教之则幸矣。丁酉正月二十四日。乃函丈初忌也。为参祀事。以二十二日。留斋于书斋。大源与士正,汝直。黄昏后来访。明灯打话。夜分后归。(二十三日。乃函丈先妣忌祀。故为行祀事归去。不得联枕。)此时有多少说话。及至二十四日过祀事后。有白丈奠诔之论。其规模物色。与甲午冬龙溪之会疏卞事。恰如一板印出。而疏卞事较大。此事甚小。小者大之影。而大者难知。小者易见。故欲因此发端。引而申之。以为讲论之地。以书问之。盖欲明虚伪之风之所以然者而已。
附尹敬庵书
书中缕缕。深认不鄙之意。亦有合于前辈有疑相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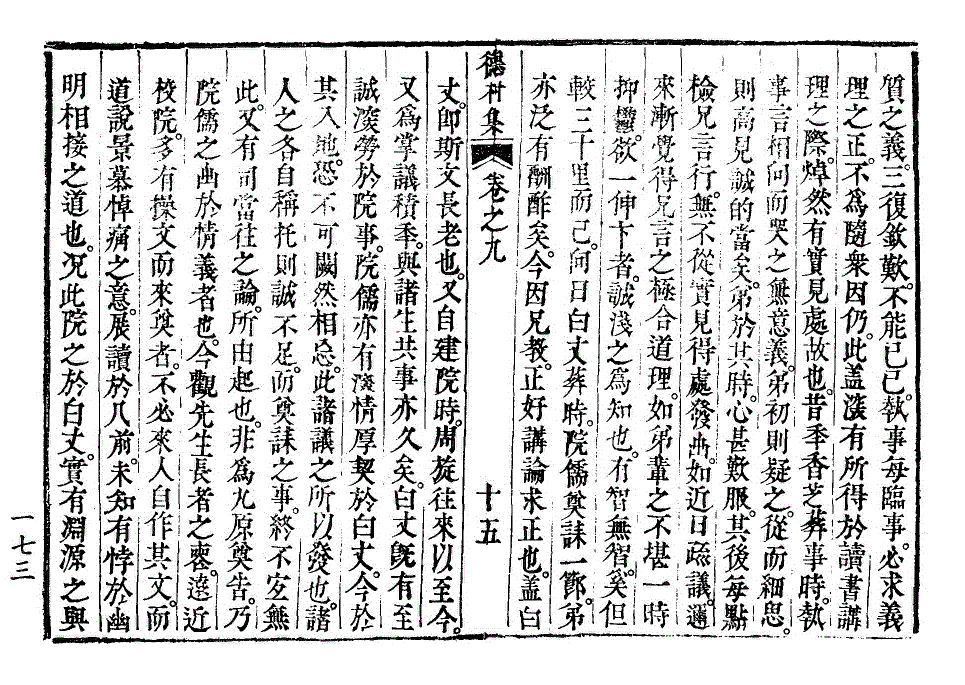 质之义。三复钦叹。不能已已。执事每临事。必求义理之正。不为随众因仍。此盖深有所得于读书讲理之际。焯然有实见处故也。昔年香芝葬事时。执事言相向而哭之无意义。弟初则疑之。从而细思。则高见诚的当矣。弟于其时。心甚叹服。其后每点检兄言行。无不从实见得处发出。如近日疏议。迩来渐觉得兄言之极合道理。如弟辈之不堪一时抑郁。欲一伸卞者。诚浅之为知也。有智无智。奚但较三十里而已。向日白丈葬时。院儒奠诔一节。弟亦泛有酬酢矣。今因兄教。正好讲论求正也。盖白丈。即斯文长老也。又自建院时。周旋往来以至今。又为掌议积年。与诸生共事亦久矣。白丈既有至诚深劳于院事。院儒亦有深情厚契于白丈。今于其入地。恐不可阙然相忘。此诸议之所以发也。诸人之各自称托则诚不足。而奠诔之事。终不宜无此。又有司当往之论。所由起也。非为九原奠告。乃院儒之出于情义者也。今观先生长者之丧。远近校院。多有操文而来奠者。不必来人自作其文。而道说景慕悼痛之意。展读于几前。未知有悖于幽明相接之道也。况此院之于白丈。实有渊源之与
质之义。三复钦叹。不能已已。执事每临事。必求义理之正。不为随众因仍。此盖深有所得于读书讲理之际。焯然有实见处故也。昔年香芝葬事时。执事言相向而哭之无意义。弟初则疑之。从而细思。则高见诚的当矣。弟于其时。心甚叹服。其后每点检兄言行。无不从实见得处发出。如近日疏议。迩来渐觉得兄言之极合道理。如弟辈之不堪一时抑郁。欲一伸卞者。诚浅之为知也。有智无智。奚但较三十里而已。向日白丈葬时。院儒奠诔一节。弟亦泛有酬酢矣。今因兄教。正好讲论求正也。盖白丈。即斯文长老也。又自建院时。周旋往来以至今。又为掌议积年。与诸生共事亦久矣。白丈既有至诚深劳于院事。院儒亦有深情厚契于白丈。今于其入地。恐不可阙然相忘。此诸议之所以发也。诸人之各自称托则诚不足。而奠诔之事。终不宜无此。又有司当往之论。所由起也。非为九原奠告。乃院儒之出于情义者也。今观先生长者之丧。远近校院。多有操文而来奠者。不必来人自作其文。而道说景慕悼痛之意。展读于几前。未知有悖于幽明相接之道也。况此院之于白丈。实有渊源之与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4H 页
 同。情契之交深。有如右所陈者乎。当初院儒已发奠告之议。非其日之猝发也。诸人之各言有故。以其窆期之进定。自虑骑率有难猝备。初非不欲往也。则谓之为他人劝送。谓之若官事之勒定者。亦恐未悉其本情也。鄙意此事似有合于情义矣。来教如此。岂迷识有所见不到而然耶。当更入思量。而亦望反复弟言。又有以批诲也。来教所谓意见趋向。不免时有不相值者。只缘平日阙讲论之益云者。诚哉言乎。若果随事讲磨。随言磋切。则始或参差而终归烂熳。何尝有不相值之虑乎。然两心相照。两情交孚。则言议之小异。不害于大体之相同。都事唯诺。亦非朋友之义矣。至于言议之枘凿。宜在斥绝之列云者。是何言也。区区之托契于高明。实有师友希文之义。所以诚信而深敬者。实不寻常矣。迷钝之见。或不能无异同。及闻高明之议。未尝不欲舍己而从之。岂敢有一毫自外之意哉。士正诸人则所敬信于执事者。实与弟一般矣。今此全不相悉之教。愚恐执事之反有不相悉者矣。噫。满纸情教蔼然。有古人朋友之义。不佞之得此于高明。奚啻万幸而已。更愿从今以往。率是无改。
同。情契之交深。有如右所陈者乎。当初院儒已发奠告之议。非其日之猝发也。诸人之各言有故。以其窆期之进定。自虑骑率有难猝备。初非不欲往也。则谓之为他人劝送。谓之若官事之勒定者。亦恐未悉其本情也。鄙意此事似有合于情义矣。来教如此。岂迷识有所见不到而然耶。当更入思量。而亦望反复弟言。又有以批诲也。来教所谓意见趋向。不免时有不相值者。只缘平日阙讲论之益云者。诚哉言乎。若果随事讲磨。随言磋切。则始或参差而终归烂熳。何尝有不相值之虑乎。然两心相照。两情交孚。则言议之小异。不害于大体之相同。都事唯诺。亦非朋友之义矣。至于言议之枘凿。宜在斥绝之列云者。是何言也。区区之托契于高明。实有师友希文之义。所以诚信而深敬者。实不寻常矣。迷钝之见。或不能无异同。及闻高明之议。未尝不欲舍己而从之。岂敢有一毫自外之意哉。士正诸人则所敬信于执事者。实与弟一般矣。今此全不相悉之教。愚恐执事之反有不相悉者矣。噫。满纸情教蔼然。有古人朋友之义。不佞之得此于高明。奚啻万幸而已。更愿从今以往。率是无改。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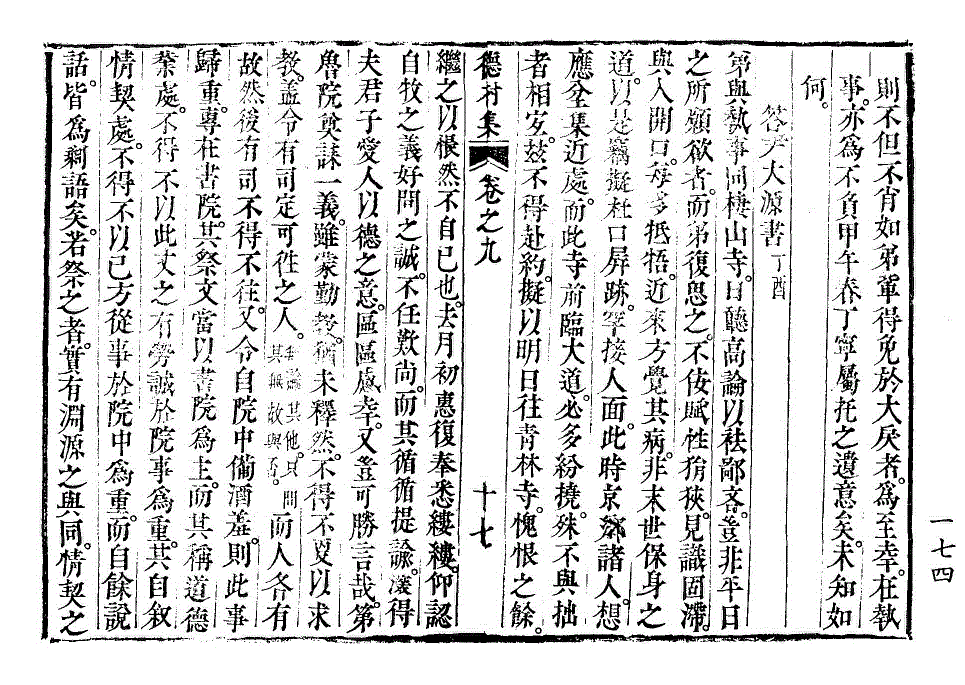 则不但不肖如弟辈得免于大戾者。为至幸。在执事。亦为不负甲午春丁宁属托之遗意矣。未知如何。
则不但不肖如弟辈得免于大戾者。为至幸。在执事。亦为不负甲午春丁宁属托之遗意矣。未知如何。答尹大源书(丁酉)
弟与执事同栖山寺。日听高论以袪鄙吝。岂非平日之所愿欲者。而弟复思之。不佞赋性狷狭。见识固滞。与人开口。每多牴牾。近来方觉其病。非末世保身之道。以是窃拟杜口屏迹。罕接人面。此时京乡诸人。想应坌集近处。而此寺前临大道。必多纷挠。殊不与拙者相宜。玆不得赴约。拟以明日往青林寺。愧恨之馀。继之以怅然不自已也。去月初惠复奉悉缕缕。仰认自牧之义好问之诚。不任叹尚。而其循循提谕。深得夫君子爱人以德之意。区区感幸。又岂可胜言哉。第鲁院奠诔一义。虽蒙勤教。犹未释然。不得不更以求教。盖令有司定可往之人。(无论其他。只问其无故与否。)而人各有故然后有司不得不往。又令自院中备酒羞。则此事归重。专在书院。其祭文当以书院为主。而其称道德业处。不得不以此丈之有劳诚于院事为重。其自叙情契处。不得不以己方从事于院中为重。而自馀说话。皆为剩语矣。若祭之者。实有渊源之与同。情契之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5H 页
 交深。(渊源情契。不可以此丈曾为此院掌议。己方从事于院中而轻以语之也。)则此事所系。非友朋则师生。其祭文当以契义为主。而此丈之有劳诚于院事。只可历举于德业称道之一端而已。若又因院事而有相从讲磨之益。则亦可备情契来历之一端而已。决不当系之书院而自院中备酒羞也。由后之说。(朋友师生契义为主。)则自是人生日用通行之常事。固无可言者。由前之说。(院中备酒羞。令有司往。借文于人。以书院为主。)则亦似粗成别一事体。而但院儒固非一人。情契尽有深浅。而未定可往之人。悬空作文于人。不论情契浅深。一以院儒概之。取酒羞于库直。借祭文于何人。是书院遣之也。非己之自往也。此吾所谓此事归重。专在书院也。即前书所谓有若官事之勒定者然也。吾未知当日之携其奠操其文而往哭者。其心果自以为申己之情否耶。其人苟有一分情契之别于众人。则势当了此一奠之后。又自备奠羞。自作祭文而哭之。然后方是恔于其心。(设以身处之。似不得不然。)然则前之一奠。非为书院奠告而何所当耶。前书所谓为九原先辈。奠告于后死者之灵。于义无稽者此也。然而其文必不曰书院谨遣某云。而曰院儒某敢告云。则揆以情文。不几于半上落下耶。先生长者之丧。远近校院。多
交深。(渊源情契。不可以此丈曾为此院掌议。己方从事于院中而轻以语之也。)则此事所系。非友朋则师生。其祭文当以契义为主。而此丈之有劳诚于院事。只可历举于德业称道之一端而已。若又因院事而有相从讲磨之益。则亦可备情契来历之一端而已。决不当系之书院而自院中备酒羞也。由后之说。(朋友师生契义为主。)则自是人生日用通行之常事。固无可言者。由前之说。(院中备酒羞。令有司往。借文于人。以书院为主。)则亦似粗成别一事体。而但院儒固非一人。情契尽有深浅。而未定可往之人。悬空作文于人。不论情契浅深。一以院儒概之。取酒羞于库直。借祭文于何人。是书院遣之也。非己之自往也。此吾所谓此事归重。专在书院也。即前书所谓有若官事之勒定者然也。吾未知当日之携其奠操其文而往哭者。其心果自以为申己之情否耶。其人苟有一分情契之别于众人。则势当了此一奠之后。又自备奠羞。自作祭文而哭之。然后方是恔于其心。(设以身处之。似不得不然。)然则前之一奠。非为书院奠告而何所当耶。前书所谓为九原先辈。奠告于后死者之灵。于义无稽者此也。然而其文必不曰书院谨遣某云。而曰院儒某敢告云。则揆以情文。不几于半上落下耶。先生长者之丧。远近校院。多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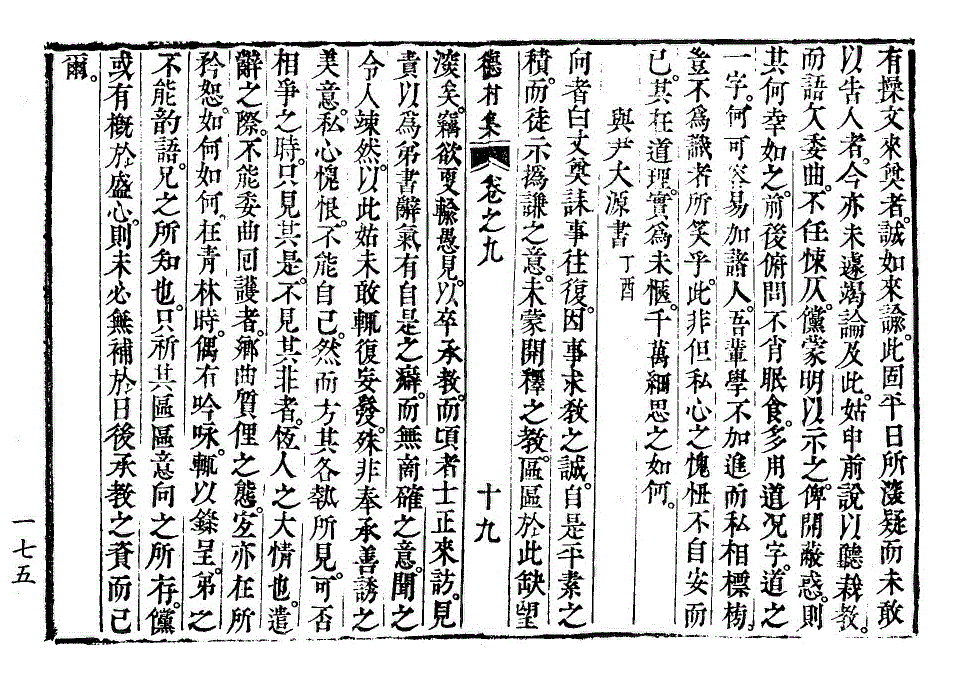 有操文来奠者。诚如来谕。此固平日所深疑而未敢以告人者。今亦未遽竭论及此。姑申前说以听栽教。而语欠委曲。不任悚仄。傥蒙明以示之。俾开蔽惑。则其何幸如之。前后俯问不肖眠食。多用道况字。道之一字。何可容易加诸人。吾辈学不加进而私相标榜。岂不为识者所笑乎。此非但私心之愧忸不自安而已。其在道理。实为未惬。千万细思之如何。
有操文来奠者。诚如来谕。此固平日所深疑而未敢以告人者。今亦未遽竭论及此。姑申前说以听栽教。而语欠委曲。不任悚仄。傥蒙明以示之。俾开蔽惑。则其何幸如之。前后俯问不肖眠食。多用道况字。道之一字。何可容易加诸人。吾辈学不加进而私相标榜。岂不为识者所笑乎。此非但私心之愧忸不自安而已。其在道理。实为未惬。千万细思之如何。与尹大源书(丁酉)
向者白丈奠诔事往复。因事求教之诚。自是平素之积。而徒示撝谦之意。未蒙开释之教。区区于此缺望深矣。窃欲更输愚见。以卒承教。而顷者士正来访。见责以为弟书辞气有自是之癖。而无商确之意。闻之令人竦然。以此姑未敢辄复妄发。殊非奉承善诱之美意。私心愧恨。不能自已。然而方其各执所见。可否相争之时。只见其是。不见其非者。恒人之大情也。遣辞之际。不能委曲回护者。乡曲质俚之态。宜亦在所矜恕。如何如何。在青林时。偶有吟咏。辄以录呈。弟之不能韵语。兄之所知也。只祈其区区意向之所存。傥或有概于盛心。则未必无补于日后承教之资而已尔。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6H 页
 附尹敬庵书
附尹敬庵书示意谨悉。此事已三辱勤质。讲教不已。于此可以知不耻下问之盛意。不以人之昏愚无解见而终弃之。不胜钦叹。第迷昧之见。实不知此事之戾于人情悖于事理矣。自承盛问。始则骇然而惑。恐高明之过于思量也。终则恍然而疑。又以为明见每临事不苟。岂其无义。缕缕若是。必吾之识。有所见不到处也。至今思之。不能得此。所以前书有欲待学进见明之语者也。近观石潭日记。则退翁之丧。馆学操文以奠。此事之有。盖已久矣。函丈亦有代撰院儒祭长老文矣。此可为今番事之依据。若曰退翁故有馆学之奠。非退翁而奠之不可云尔。则可成义理。而函丈代撰之文。则非退翁之伦矣。盖酌其轻重。致其情义。恐无不可故也。不然则前辈又何以行之耶。若又曰凡事当自度以己见。而前辈不可依据云尔。则恐自信己见之病。大于依样前辈之失矣。后生之学未明见未透者。不以前辈为法。更于何据依耶。果自谓吾学已明。吾见已透。不必依法前辈。则恐其易于狓猖自恣之归矣。此则非谓高明之如是也。或虑其流弊之至于此耳。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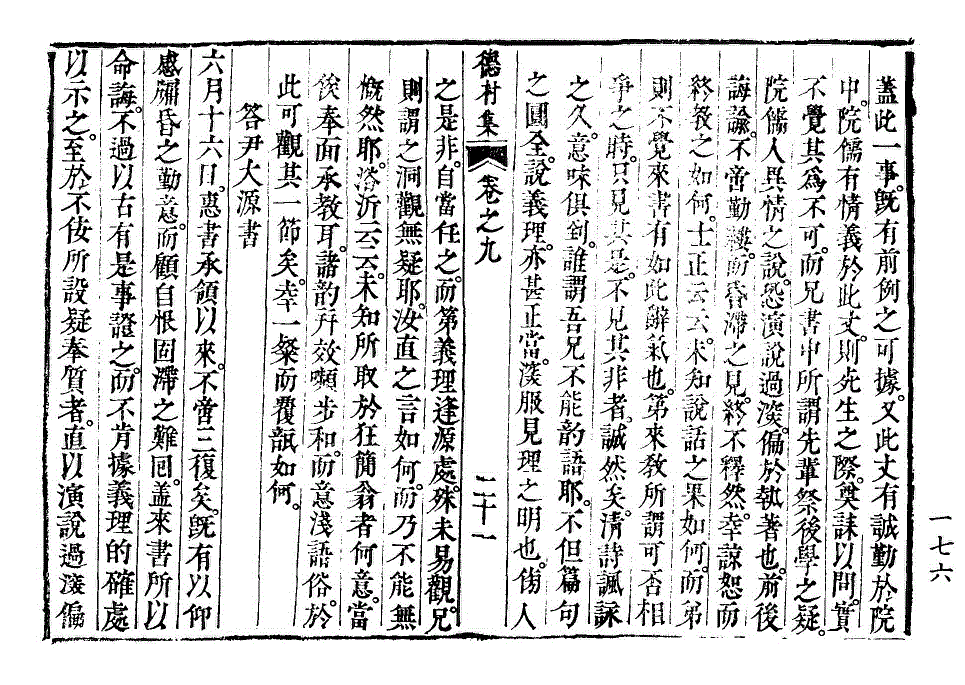 盖此一事。既有前例之可据。又此丈有诚勤于院中。院儒有情义于此丈。则死生之际。奠诔以问。实不觉其为不可。而兄书中所谓先辈祭后学之疑。院儒人异情之说。恐演说过深。偏于执著也。前后诲谕。不啻勤缕。而昏滞之见。终不释然。幸谅恕而终教之如何。士正云云。未知说话之果如何。而弟则不觉来书有如此辞气也。第来教所谓可否相争之时。只见其是。不见其非者。诚然矣。清诗讽咏之久。意味俱到。谁谓吾兄不能韵语耶。不但篇句之圆全。说义理。亦甚正当。深服见理之明也。傍人之是非。自当任之。而第义理逢源处。殊未易观。兄则谓之洞观无疑耶。汝直之言如何。而乃不能无慨然耶。浴沂云云。未知所取于狂简翁者何意。当俟奉面承教耳。诸韵并效嚬步和。而意浅语俗。于此可观其一节矣。幸一粲而覆瓿如何。
盖此一事。既有前例之可据。又此丈有诚勤于院中。院儒有情义于此丈。则死生之际。奠诔以问。实不觉其为不可。而兄书中所谓先辈祭后学之疑。院儒人异情之说。恐演说过深。偏于执著也。前后诲谕。不啻勤缕。而昏滞之见。终不释然。幸谅恕而终教之如何。士正云云。未知说话之果如何。而弟则不觉来书有如此辞气也。第来教所谓可否相争之时。只见其是。不见其非者。诚然矣。清诗讽咏之久。意味俱到。谁谓吾兄不能韵语耶。不但篇句之圆全。说义理。亦甚正当。深服见理之明也。傍人之是非。自当任之。而第义理逢源处。殊未易观。兄则谓之洞观无疑耶。汝直之言如何。而乃不能无慨然耶。浴沂云云。未知所取于狂简翁者何意。当俟奉面承教耳。诸韵并效嚬步和。而意浅语俗。于此可观其一节矣。幸一粲而覆瓿如何。答尹大源书
六月十六日。惠书承领以来。不啻三复矣。既有以仰感牖昏之勤意。而顾自恨固滞之难回。盖来书所以命诲。不过以古有是事證之。而不肯据义理的确处以示之。至于不佞所设疑奉质者。直以演说过深偏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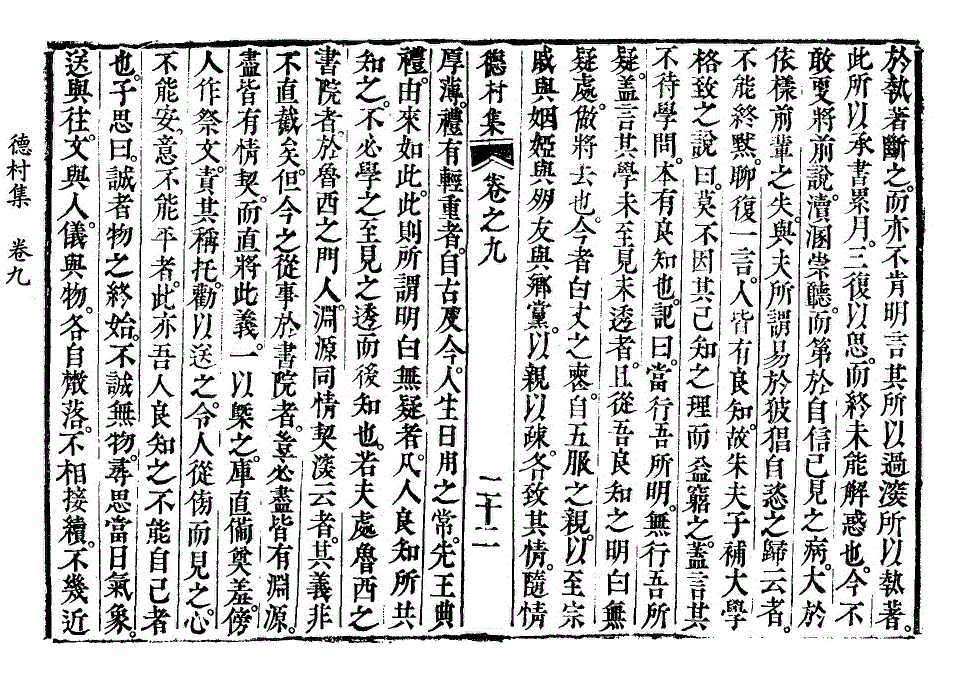 于执著断之。而亦不肯明言其所以过深所以执著。此所以承书累月。三复以思。而终未能解惑也。今不敢更将前说。渎溷崇听。而第于自信己见之病。大于依样前辈之失。与夫所谓易于狓猖自恣之归云者。不能终默。聊复一言。人皆有良知。故朱夫子补大学格致之说曰。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盖言其不待学问。本有良知也。记曰。当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盖言其学未至见未透者。且从吾良知之明白无疑处。做将去也。今者白丈之丧。自五服之亲。以至宗戚与姻娅与朋友与乡党。以亲以疏。各致其情。随情厚薄。礼有轻重者。自古及今。人生日用之常。先王典礼。由来如此。此则所谓明白无疑者。凡人良知所共知之。不必学之至见之透而后知也。若夫处鲁西之书院者。于鲁西之门人。渊源同情契深云者。其义非不直截矣。但今之从事于书院者。岂必尽皆有渊源。尽皆有情契。而直将此义。一以槩之。库直备奠羞。傍人作祭文。责其称托。劝以送之。令人从傍而见之。心不能安。意不能平者。此亦吾人良知之不能自已者也。子思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寻思当日气象。送与往。文与人。仪与物。各自散落。不相接续。不几近
于执著断之。而亦不肯明言其所以过深所以执著。此所以承书累月。三复以思。而终未能解惑也。今不敢更将前说。渎溷崇听。而第于自信己见之病。大于依样前辈之失。与夫所谓易于狓猖自恣之归云者。不能终默。聊复一言。人皆有良知。故朱夫子补大学格致之说曰。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盖言其不待学问。本有良知也。记曰。当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盖言其学未至见未透者。且从吾良知之明白无疑处。做将去也。今者白丈之丧。自五服之亲。以至宗戚与姻娅与朋友与乡党。以亲以疏。各致其情。随情厚薄。礼有轻重者。自古及今。人生日用之常。先王典礼。由来如此。此则所谓明白无疑者。凡人良知所共知之。不必学之至见之透而后知也。若夫处鲁西之书院者。于鲁西之门人。渊源同情契深云者。其义非不直截矣。但今之从事于书院者。岂必尽皆有渊源。尽皆有情契。而直将此义。一以槩之。库直备奠羞。傍人作祭文。责其称托。劝以送之。令人从傍而见之。心不能安。意不能平者。此亦吾人良知之不能自已者也。子思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寻思当日气象。送与往。文与人。仪与物。各自散落。不相接续。不几近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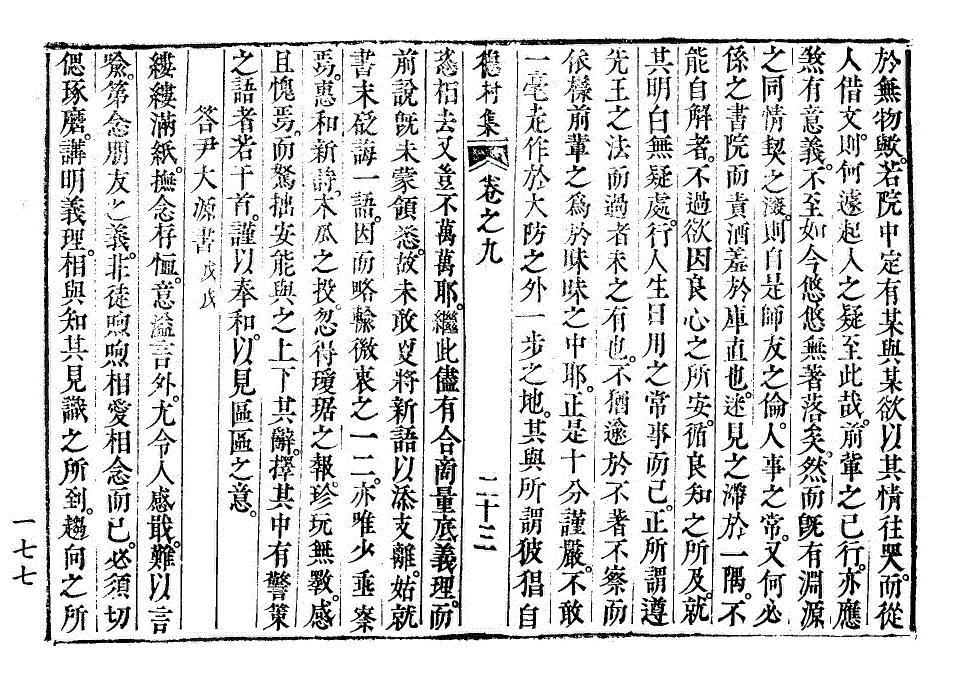 于无物欤。若院中定有某与某欲以其情往哭。而从人借文。则何遽起人之疑至此哉。前辈之已行。亦应煞有意义。不至如今悠悠无著落矣。然而既有渊源之同情契之深。则自是师友之伦。人事之常。又何必系之书院而责酒羞于库直也。迷见之滞于一隅。不能自解者。不过欲因良心之所安。循良知之所及。就其明白无疑处。行人生日用之常事而已。正所谓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不犹逾于不著不察而依样前辈之为于昧昧之中耶。正是十分谨严。不敢一毫走作于大防之外一步之地。其与所谓狓猖自恣相去又岂不万万耶。继此尽有合商量底义理。而前说既未蒙领悉。故未敢更将新语以添支离。姑就书末砭诲一语。因而略输微衷之一二。亦唯少垂察焉。惠和新诗。木瓜之投。忽得琼琚之报。珍玩无斁。感且愧焉。而驽拙安能与之上下其辞。择其中有警策之语者若干首。谨以奉和。以见区区之意。
于无物欤。若院中定有某与某欲以其情往哭。而从人借文。则何遽起人之疑至此哉。前辈之已行。亦应煞有意义。不至如今悠悠无著落矣。然而既有渊源之同情契之深。则自是师友之伦。人事之常。又何必系之书院而责酒羞于库直也。迷见之滞于一隅。不能自解者。不过欲因良心之所安。循良知之所及。就其明白无疑处。行人生日用之常事而已。正所谓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不犹逾于不著不察而依样前辈之为于昧昧之中耶。正是十分谨严。不敢一毫走作于大防之外一步之地。其与所谓狓猖自恣相去又岂不万万耶。继此尽有合商量底义理。而前说既未蒙领悉。故未敢更将新语以添支离。姑就书末砭诲一语。因而略输微衷之一二。亦唯少垂察焉。惠和新诗。木瓜之投。忽得琼琚之报。珍玩无斁。感且愧焉。而驽拙安能与之上下其辞。择其中有警策之语者若干首。谨以奉和。以见区区之意。答尹大源书(戊戌)
缕缕满纸。抚念存恤。意溢言外。尤令人感戢。难以言喻。第念朋友之义。非徒喣喣相爱相念而已。必须切偲琢磨。讲明义理。相与知其见识之所到。趋向之所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8H 页
 归。然后始可以言相知矣。相知既深。则其义自重。常思古语。士为知己用。直须与女为悦己容作对。盖言其理势自然。不假貌为也。窃见诸贤之于言议之际。不先讲明义理之所安。使之各尽其意见之所极。而径自较计于同异之际。以为从违之断。是以义理未明而疑阻先生。弟诚不佞。深所未晓。区区之于诸贤。每以不相悉奉告者。非敢有间于同异之际也。只为言议之不苟同。正是吾辈之事。义理讲明。正在其中。而诸贤之于不佞。不问义理与意见之如何。每将同异之说。缱绻不置。或谓之宜同而不宜异。或谓之少异无害于大同。亦尝见自古朋友讲论。有如此物色乎。悠悠流俗。固无可言。而吾辈规模。诚亦可羞。向者白丈奠诔事往复。非故立异而务胜也。但以因此一事。尽意讨论。则彼此意见。可以相悉。而义理之实。因亦可明。区区本意。诚非偶然。去年冬一书。几于倾倒愚衷。而此岁将尽。未蒙俯答。私心泄泄。不可胜言。抑无乃辞意鹘突。近于自是。有如曩者士正所见责者。故姑为此不屑之教耶。然而质俚之态。向已伏其辜矣。幸须特赐宽恕。终遂教之。不胜千万之幸。净寺之会。虽未能久留承诲。或可乘隙一进来会之后。即为
归。然后始可以言相知矣。相知既深。则其义自重。常思古语。士为知己用。直须与女为悦己容作对。盖言其理势自然。不假貌为也。窃见诸贤之于言议之际。不先讲明义理之所安。使之各尽其意见之所极。而径自较计于同异之际。以为从违之断。是以义理未明而疑阻先生。弟诚不佞。深所未晓。区区之于诸贤。每以不相悉奉告者。非敢有间于同异之际也。只为言议之不苟同。正是吾辈之事。义理讲明。正在其中。而诸贤之于不佞。不问义理与意见之如何。每将同异之说。缱绻不置。或谓之宜同而不宜异。或谓之少异无害于大同。亦尝见自古朋友讲论。有如此物色乎。悠悠流俗。固无可言。而吾辈规模。诚亦可羞。向者白丈奠诔事往复。非故立异而务胜也。但以因此一事。尽意讨论。则彼此意见。可以相悉。而义理之实。因亦可明。区区本意。诚非偶然。去年冬一书。几于倾倒愚衷。而此岁将尽。未蒙俯答。私心泄泄。不可胜言。抑无乃辞意鹘突。近于自是。有如曩者士正所见责者。故姑为此不屑之教耶。然而质俚之态。向已伏其辜矣。幸须特赐宽恕。终遂教之。不胜千万之幸。净寺之会。虽未能久留承诲。或可乘隙一进来会之后。即为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8L 页
 示知如何。
示知如何。与尹大源书(己亥)
向日奉复。开端而未尽。复此布之。愿卒承教。不佞于诸贤。非敢以友道自处。责善自任也。只以不佞。猥以无似。厕在朋友之列。而诸贤之所以处不佞者。于区区之心。每不相悉。故欲因事讲义。表见心曲。庶祈诸贤俯谅微衷。免使此身临事臲卼而已。然前此非无此心。而到今始有讲质者。抑亦有说。窃尝见此中章甫别有一种之义。已作大同之俗。流来已久。自成规模。众所趋赴。无敢异同。意见小有出人形迹。便成疑贰。不佞盖创见而心怪之。亦尝累示微意。试开讲论之端。则非徒邈不采听。乃反勒以情外。似此风习。关系不轻。欲出气救正。则非力量所及。欲黾勉随众。则非本心所安。宁欲泯泯没没。不见数于章甫间言议之中。而此亦不可得矣。是以于其小且歇处。不免随众因仍。于其大且紧处。不得不守己所见。如此如此。荀然以度。外循内顾。无非可吝。中夜以思。仰屋窃叹而已。然而因此渐见疏外。令诸贤知其为无用之物而遂弃之。则亦可以自在食息。自在读书。浩然而自得矣。隐然一念。不无祈望于此。而诸贤犹不肯全舍。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9H 页
 则亦无如之何矣。于是乎复慨然以为道若大路。本自平易。何为拘挛。自取窘步。遂欲随事禀疑。不复如前日之因仍苟且。庶几理明心白。有所底至。适此白丈奠诔一事。在于鄙心。颇未相契。故乃敢因此发端。有所往复。原其本心。不过自为之地而已。非有一毫晓人底意思也。然而既以所疑奉质。则系是朋友间讲说。亦当叩其两端。剖其条理。使其惑开而疑释。不宜直以前辈已行而令人不敢致疑于其间也。况义理精微尽无穷。又安知夫同行异情。不在毫釐之间耶。渊源情契。舍师友则无著处。师友间死生之问。自有先王典礼。民俗通行。渊源情契。有浅深。故死生之问。其礼亦自有轻重浅深轻重。各自称情。是之谓节文。是之谓仪则。非可一毫容私。亦非人所可劝沮。院儒非一人。而未有主往。悬空作文。是无轻重之分矣。轻重之间。惟一有司奔走。有司又为人所劝。渊源情契。果如是乎。节文仪则。何所当乎。鄙心所疑。在此一著。于此一著。一言开示。岂不快哉。来书谓此院之于白丈。实有渊源之与同。情契之交深云云。不曰某人而直曰此院。盖谓从事此院者。皆有渊源。皆有情契云尔。审如是则悬空作文。亦未为不可。而但许多渊
则亦无如之何矣。于是乎复慨然以为道若大路。本自平易。何为拘挛。自取窘步。遂欲随事禀疑。不复如前日之因仍苟且。庶几理明心白。有所底至。适此白丈奠诔一事。在于鄙心。颇未相契。故乃敢因此发端。有所往复。原其本心。不过自为之地而已。非有一毫晓人底意思也。然而既以所疑奉质。则系是朋友间讲说。亦当叩其两端。剖其条理。使其惑开而疑释。不宜直以前辈已行而令人不敢致疑于其间也。况义理精微尽无穷。又安知夫同行异情。不在毫釐之间耶。渊源情契。舍师友则无著处。师友间死生之问。自有先王典礼。民俗通行。渊源情契。有浅深。故死生之问。其礼亦自有轻重浅深轻重。各自称情。是之谓节文。是之谓仪则。非可一毫容私。亦非人所可劝沮。院儒非一人。而未有主往。悬空作文。是无轻重之分矣。轻重之间。惟一有司奔走。有司又为人所劝。渊源情契。果如是乎。节文仪则。何所当乎。鄙心所疑。在此一著。于此一著。一言开示。岂不快哉。来书谓此院之于白丈。实有渊源之与同。情契之交深云云。不曰某人而直曰此院。盖谓从事此院者。皆有渊源。皆有情契云尔。审如是则悬空作文。亦未为不可。而但许多渊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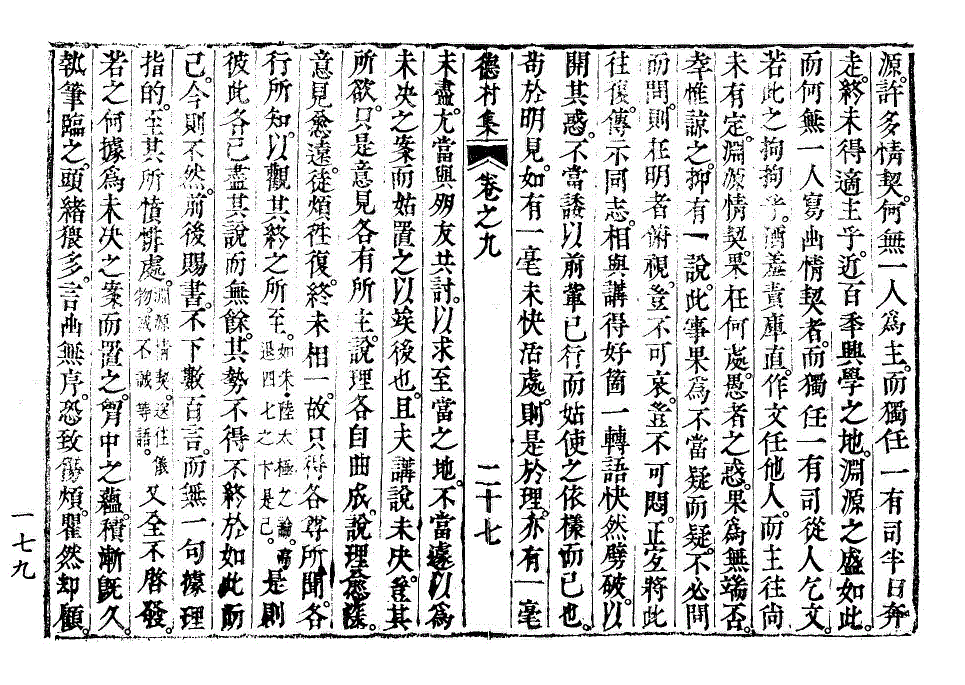 源。许多情契。何无一人为主。而独任一有司半日奔走。终未得适主乎。近百年兴学之地。渊源之盛如此。而何无一人写出情契者。而独任一有司从人乞文。若此之拘拘乎。酒羞责库直。作文任他人。而主往尚未有定。渊源情契。果在何处。愚者之惑。果为无端否。幸惟谅之。抑有一说。此事果为不当疑而疑。不必问而问。则在明者俯视。岂不可哀。岂不可闷。正宜将此往复。传示同志。相与讲得好个一转语快然劈破。以开其惑。不当诿以前辈已行而姑使之依样而已也。苟于明见。如有一毫未快活处。则是于理。亦有一毫未尽。尤当与朋友共讨。以求至当之地。不当遽以为未决之案而姑置之以俟后也。且夫讲说未决。岂其所欲。只是意见各有所主。说理各自曲成。说理愈深。意见愈远。徒烦往复。终未相一。故只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以观其终之所至。(如朱,陆太极之论。高,退四七之卞是已。)是则彼此各已尽其说而无馀。其势不得不终于如此而已。今则不然。前后赐书。不下数百言。而无一句据理指的。至其所愤悱处。(渊源情契。送往仪物。或不诚等语。)又全不启发。若之何据为未决之案而置之。胸中之蕴。积渐既久。执笔临之。头绪猥多。言出无序。恐致伤烦。瞿然却顾。
源。许多情契。何无一人为主。而独任一有司半日奔走。终未得适主乎。近百年兴学之地。渊源之盛如此。而何无一人写出情契者。而独任一有司从人乞文。若此之拘拘乎。酒羞责库直。作文任他人。而主往尚未有定。渊源情契。果在何处。愚者之惑。果为无端否。幸惟谅之。抑有一说。此事果为不当疑而疑。不必问而问。则在明者俯视。岂不可哀。岂不可闷。正宜将此往复。传示同志。相与讲得好个一转语快然劈破。以开其惑。不当诿以前辈已行而姑使之依样而已也。苟于明见。如有一毫未快活处。则是于理。亦有一毫未尽。尤当与朋友共讨。以求至当之地。不当遽以为未决之案而姑置之以俟后也。且夫讲说未决。岂其所欲。只是意见各有所主。说理各自曲成。说理愈深。意见愈远。徒烦往复。终未相一。故只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以观其终之所至。(如朱,陆太极之论。高,退四七之卞是已。)是则彼此各已尽其说而无馀。其势不得不终于如此而已。今则不然。前后赐书。不下数百言。而无一句据理指的。至其所愤悱处。(渊源情契。送往仪物。或不诚等语。)又全不启发。若之何据为未决之案而置之。胸中之蕴。积渐既久。执笔临之。头绪猥多。言出无序。恐致伤烦。瞿然却顾。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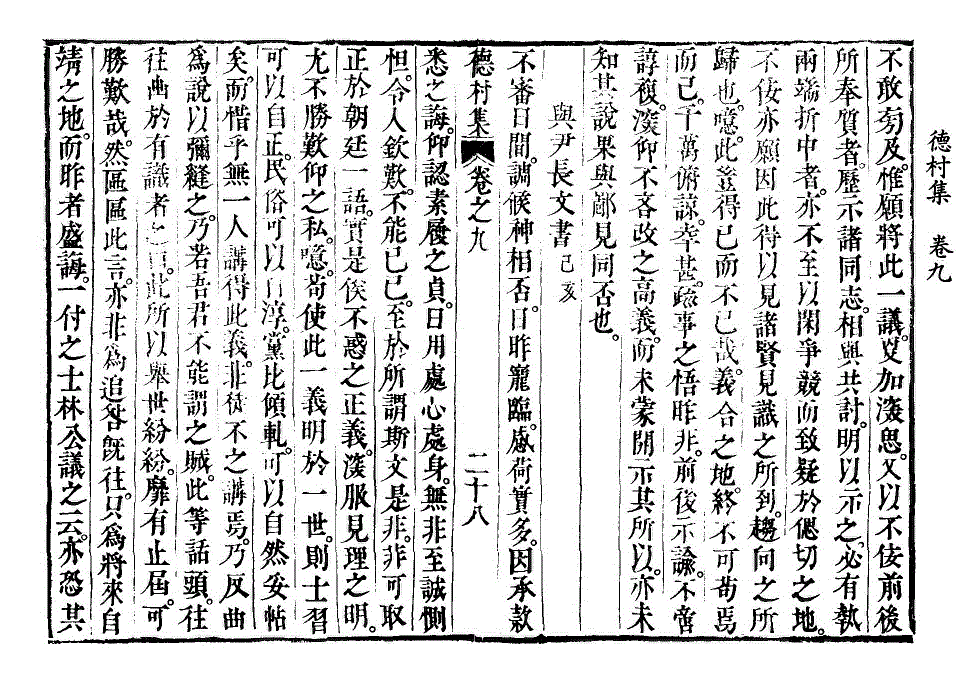 不敢旁及。惟愿将此一议。更加深思。又以不佞前后所奉质者。历示诸同志。相与共讨。明以示之。必有执两端折中者。亦不至以闲争竞而致疑于偲切之地。不佞亦愿因此得以见诸贤见识之所到。趋向之所归也。噫。此岂得已而不已哉。义合之地。终不可苟焉而已。千万俯谅。幸甚。疏事之悟昨非。前后示谕。不啻谆复。深仰不吝改之高义。而未蒙开示其所以。亦未知其说果与鄙见同否也。
不敢旁及。惟愿将此一议。更加深思。又以不佞前后所奉质者。历示诸同志。相与共讨。明以示之。必有执两端折中者。亦不至以闲争竞而致疑于偲切之地。不佞亦愿因此得以见诸贤见识之所到。趋向之所归也。噫。此岂得已而不已哉。义合之地。终不可苟焉而已。千万俯谅。幸甚。疏事之悟昨非。前后示谕。不啻谆复。深仰不吝改之高义。而未蒙开示其所以。亦未知其说果与鄙见同否也。与尹长文书(己亥)
不审日间。调候神相否。日昨宠临。感荷实多。因承款悉之诲。仰认素履之贞。日用处心处身。无非至诚恻怛。令人钦叹。不能已已。至于所谓斯文是非。非可取正于朝廷一语。实是俟不惑之正义。深服见理之明。尤不胜叹仰之私。噫。苟使此一义明于一世。则士习可以自正。民俗可以自淳。党比倾轧。可以自然妥帖矣。而惜乎无一人讲得此义。非徒不之讲焉。乃反曲为说以弥缝之。乃若吾君不能谓之贼。此等话头。往往出于有识者之口。此所以举世纷纷。靡有止届。可胜叹哉。然区区此言。亦非为追咎既往。只为将来自靖之地。而昨者盛诲。一付之士林公议之云。亦恐其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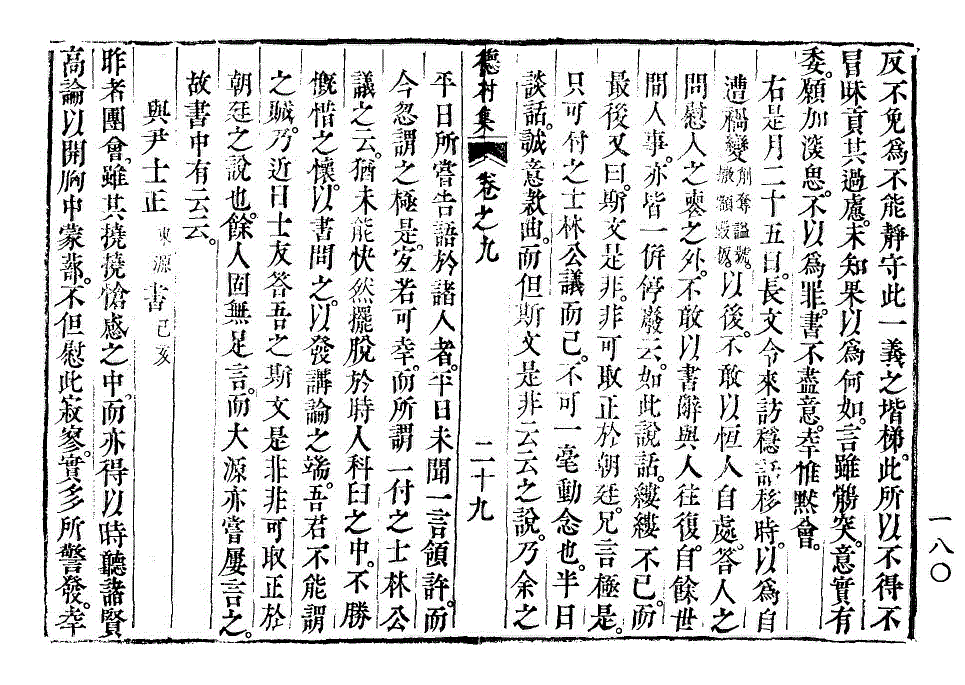 反不免为不能静守此一义之阶梯。此所以不得不冒昧贡其过虑。未知果以为何如。言虽鹘突。意实有委。愿加深思。不以为罪。书不尽意。幸惟默会。
反不免为不能静守此一义之阶梯。此所以不得不冒昧贡其过虑。未知果以为何如。言虽鹘突。意实有委。愿加深思。不以为罪。书不尽意。幸惟默会。右是月二十五日。长文令来访稳话移时。以为自遭祸变(削夺谥号。撤额毁板。)以后。不敢以恒人自处。答人之问慰人之丧之外。不敢以书辞与人往复。自馀世间人事。亦皆一并停废云。如此说话。缕缕不已。而最后又曰。斯文是非。非可取正于朝廷。兄言极是。只可付之士林公议而已。不可一毫动念也。半日谈话。诚意款曲。而但斯文是非云云之说。乃余之平日所尝告语于诸人者。平日未闻一言领许。而今忽谓之极是。宜若可幸。而所谓一付之士林公议之云。犹未能快然摆脱于时人科臼之中。不胜慨惜之怀。以书问之。以发讲论之端。吾君不能谓之贼。乃近日士友答吾之斯文是非非可取正于朝廷之说也。馀人固无足言。而大源亦尝屡言之。故书中有云云。
与尹士正(东源)书(己亥)
昨者团会。虽其挠挠怆感之中。而亦得以时听诸贤高论以开胸中蒙蔀。不但慰此寂寥。实多所警发。幸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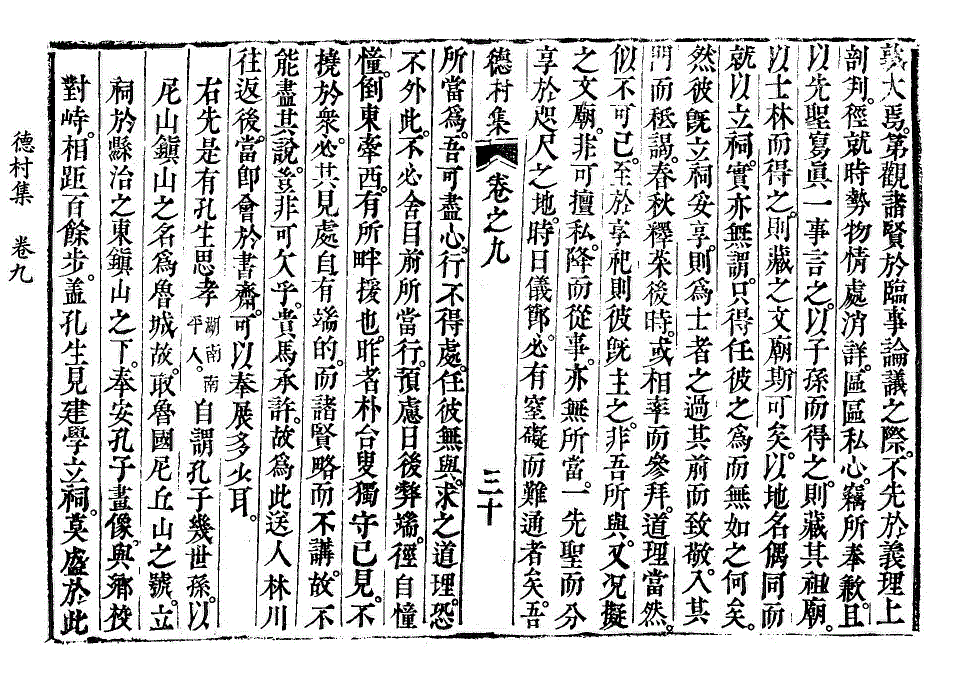 孰大焉。第观诸贤于临事论议之际。不先于义理上剖判。径就时势物情处消详。区区私心。窃所奉歉。且以先圣写真一事言之。以子孙而得之。则藏其祖庙。以士林而得之。则藏之文庙斯可矣。以地名偶同而就以立祠。实亦无谓。只得任彼之为而无如之何矣。然彼既立祠妥享。则为士者之过其前而致敬。入其门而秪谒。春秋释菜后时。或相率而参拜。道理当然。似不可已。至于享祀则彼既主之。非吾所与。又况拟之文庙。非可擅私。降而从事。亦无所当。一先圣而分享于咫尺之地。时日仪节。必有窒碍而难通者矣。吾所当为。吾可尽心。行不得处。任彼无与。求之道理。恐不外此。不必舍目前所当行。预虑日后弊端。径自憧憧。倒东牵西。有所畔援也。昨者朴台叟独守己见。不挠于众。必其见处自有端的。而诸贤略而不讲。故不能尽其说。岂非可欠乎。贵马承许。故为此送人林川往返后。当即会于书斋。可以奉展多少耳。
孰大焉。第观诸贤于临事论议之际。不先于义理上剖判。径就时势物情处消详。区区私心。窃所奉歉。且以先圣写真一事言之。以子孙而得之。则藏其祖庙。以士林而得之。则藏之文庙斯可矣。以地名偶同而就以立祠。实亦无谓。只得任彼之为而无如之何矣。然彼既立祠妥享。则为士者之过其前而致敬。入其门而秪谒。春秋释菜后时。或相率而参拜。道理当然。似不可已。至于享祀则彼既主之。非吾所与。又况拟之文庙。非可擅私。降而从事。亦无所当。一先圣而分享于咫尺之地。时日仪节。必有窒碍而难通者矣。吾所当为。吾可尽心。行不得处。任彼无与。求之道理。恐不外此。不必舍目前所当行。预虑日后弊端。径自憧憧。倒东牵西。有所畔援也。昨者朴台叟独守己见。不挠于众。必其见处自有端的。而诸贤略而不讲。故不能尽其说。岂非可欠乎。贵马承许。故为此送人林川往返后。当即会于书斋。可以奉展多少耳。右先是有孔生思孝(湖南南平人。)自谓孔子几世孙。以尼山镇山之名为鲁城故。取鲁国尼丘山之号。立祠于县治之东镇山之下。奉安孔子画像。与乡校对峙。相距百馀步。盖孔生见建学立祠。莫盛于此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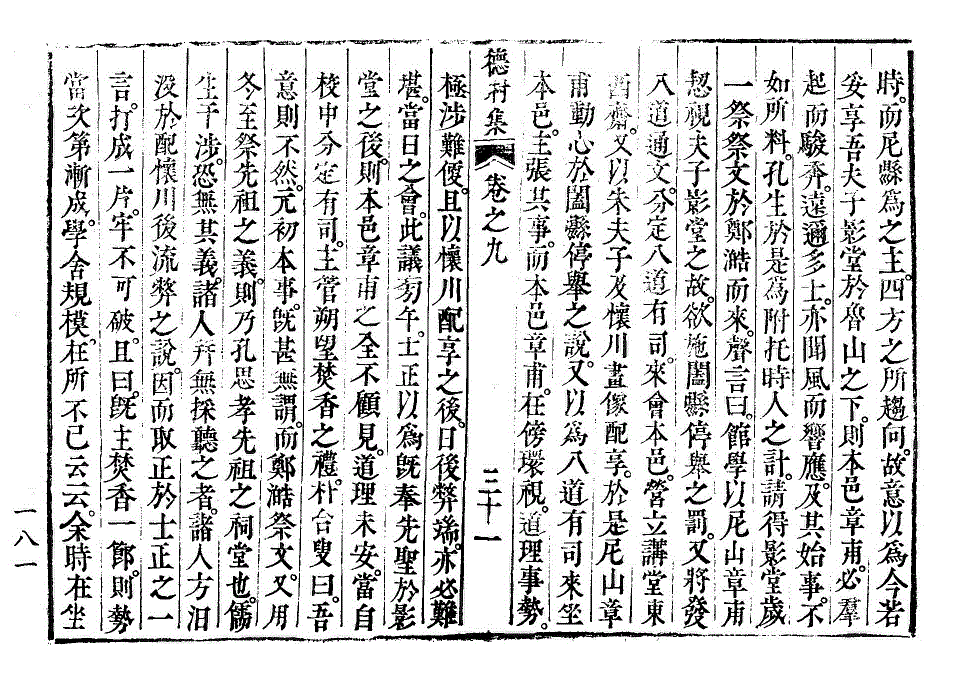 时。而尼县为之主。四方之所趋向。故意以为今若妥享吾夫子影堂于鲁山之下。则本邑章甫。必群起而骏奔。远迩多士。亦闻风而响应。及其始事。不如所料。孔生于是为附托时人之计。请得影堂岁一祭祭文于郑浩而来。声言曰。馆学以尼山章甫恝视夫子影堂之故。欲施阖县停举之罚。又将发八道通文。分定八道有司。来会本邑。营立讲堂东西斋。又以朱夫子及怀川画像配享。于是尼山章甫动心于阖县停举之说。又以为八道有司来坐本邑。主张其事。而本邑章甫。在傍环视。道理事势。极涉难便。且以怀川配享之后。日后弊端。亦必难堪。当日之会。此议旁午。士正以为既奉先圣于影堂之后。则本邑章甫之全不顾见。道理未安。当自校中分定有司。主管朔望焚香之礼。朴台叟曰。吾意则不然。元初本事。既甚无谓。而郑浩祭文。又用冬至祭先祖之义。则乃孔思孝先祖之祠堂也。儒生干涉。恐无其义。诸人并无采听之者。诸人方汩没于配怀川后流弊之说。因而取正于士正之一言。打成一片。牢不可破。且曰。既主焚香一节。则势当次第渐成。学舍规模。在所不已云云。余时在坐
时。而尼县为之主。四方之所趋向。故意以为今若妥享吾夫子影堂于鲁山之下。则本邑章甫。必群起而骏奔。远迩多士。亦闻风而响应。及其始事。不如所料。孔生于是为附托时人之计。请得影堂岁一祭祭文于郑浩而来。声言曰。馆学以尼山章甫恝视夫子影堂之故。欲施阖县停举之罚。又将发八道通文。分定八道有司。来会本邑。营立讲堂东西斋。又以朱夫子及怀川画像配享。于是尼山章甫动心于阖县停举之说。又以为八道有司来坐本邑。主张其事。而本邑章甫。在傍环视。道理事势。极涉难便。且以怀川配享之后。日后弊端。亦必难堪。当日之会。此议旁午。士正以为既奉先圣于影堂之后。则本邑章甫之全不顾见。道理未安。当自校中分定有司。主管朔望焚香之礼。朴台叟曰。吾意则不然。元初本事。既甚无谓。而郑浩祭文。又用冬至祭先祖之义。则乃孔思孝先祖之祠堂也。儒生干涉。恐无其义。诸人并无采听之者。诸人方汩没于配怀川后流弊之说。因而取正于士正之一言。打成一片。牢不可破。且曰。既主焚香一节。则势当次第渐成。学舍规模。在所不已云云。余时在坐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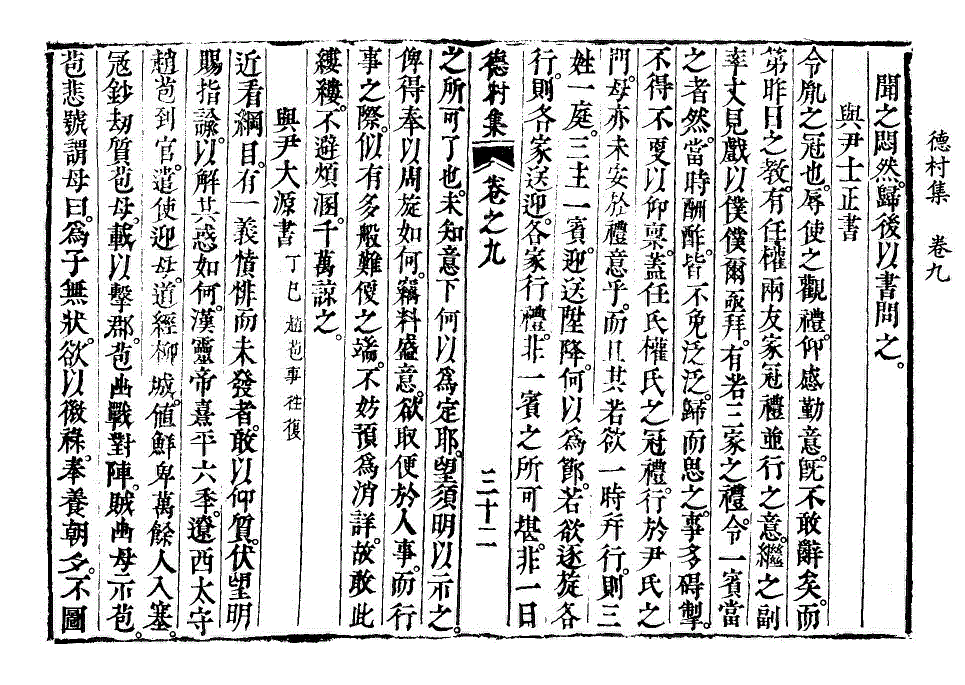 闻之闷然。归后以书问之。
闻之闷然。归后以书问之。与尹士正书
令胤之冠也。辱使之观礼。仰感勤意。既不敢辞矣。而第昨日之教。有任,权两友家冠礼并行之意。继之副率丈见戏以仆仆尔亟拜。有若三家之礼。令一宾当之者然。当时酬酢。皆不免泛泛。归而思之。事多碍掣。不得不更以仰禀。盖任氏权氏之冠礼。行于尹氏之门。毋亦未安于礼意乎。而且其若欲一时并行。则三姓一庭。三主一宾。迎送升降。何以为节。若欲逐旋各行。则各家送迎。各家行礼。非一宾之所可堪。非一日之所可了也。未知意下何以为定耶。望须明以示之。俾得奉以周旋如何。窃料盛意。欲取便于人事。而行事之际。似有多般难便之端。不妨预为消详。故敢此缕缕。不避烦溷。千万谅之。
与尹大源书(丁巳赵苞事往复)
近看纲目。有一义愤悱而未发者。敢以仰质。伏望明赐指谕。以解其惑如何。汉灵帝熹平六年。辽西太守赵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经柳城。值鲜卑万馀人入塞。寇钞劫质苞母。载以击郡。苞出战对阵。贼出母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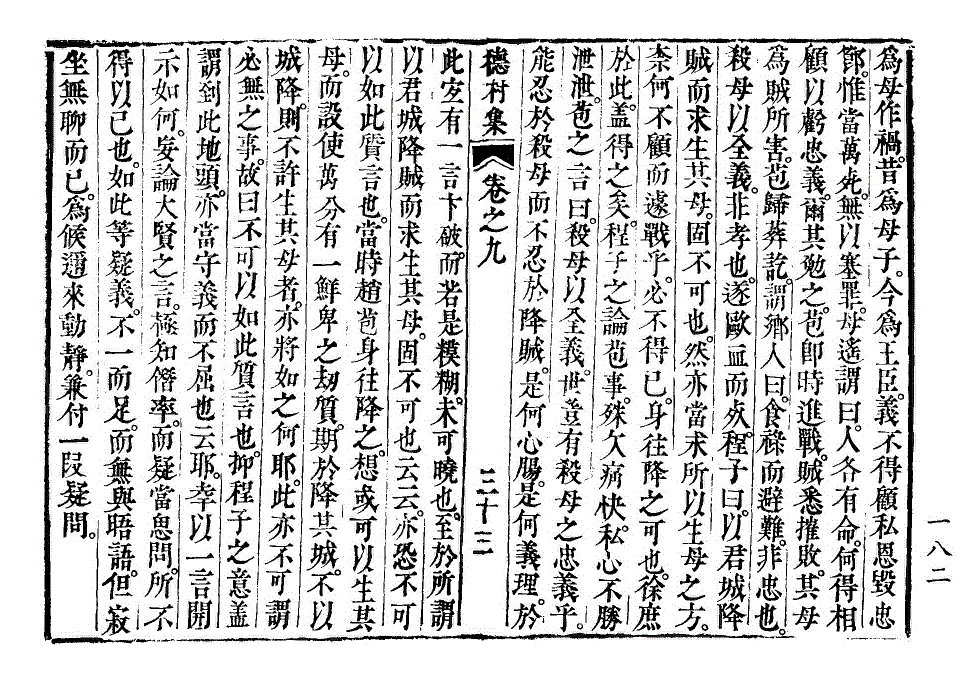 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惟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败。其母为贼所害。苞归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遂欧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固不可也。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顾而遽战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于此。盖得之矣。程子之论苞事。殊欠痛快。私心不胜泄泄。苞之言曰。杀母以全义。世岂有杀母之忠义乎。能忍于杀母而不忍于降贼。是何心肠。是何义理。于此宜有一言卞破。而若是模糊。未可晓也。至于所谓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固不可也云云。亦恐不可以如此质言也。当时赵苞身往降之。想或可以生其母。而设使万分有一鲜卑之劫质。期于降其城。不以城降。则不许生其母者。亦将如之何耶。此亦不可谓必无之事。故曰不可以如此质言也。抑程子之意盖谓到此地头。亦当守义而不屈也云耶。幸以一言开示如何。妄论大贤之言。极知僭率。而疑当思问。所不得以已也。如此等疑义。不一而足。而无与晤语。但寂坐无聊而已。为候迩来动静。兼付一段疑问。
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惟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败。其母为贼所害。苞归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遂欧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固不可也。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不顾而遽战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于此。盖得之矣。程子之论苞事。殊欠痛快。私心不胜泄泄。苞之言曰。杀母以全义。世岂有杀母之忠义乎。能忍于杀母而不忍于降贼。是何心肠。是何义理。于此宜有一言卞破。而若是模糊。未可晓也。至于所谓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固不可也云云。亦恐不可以如此质言也。当时赵苞身往降之。想或可以生其母。而设使万分有一鲜卑之劫质。期于降其城。不以城降。则不许生其母者。亦将如之何耶。此亦不可谓必无之事。故曰不可以如此质言也。抑程子之意盖谓到此地头。亦当守义而不屈也云耶。幸以一言开示如何。妄论大贤之言。极知僭率。而疑当思问。所不得以已也。如此等疑义。不一而足。而无与晤语。但寂坐无聊而已。为候迩来动静。兼付一段疑问。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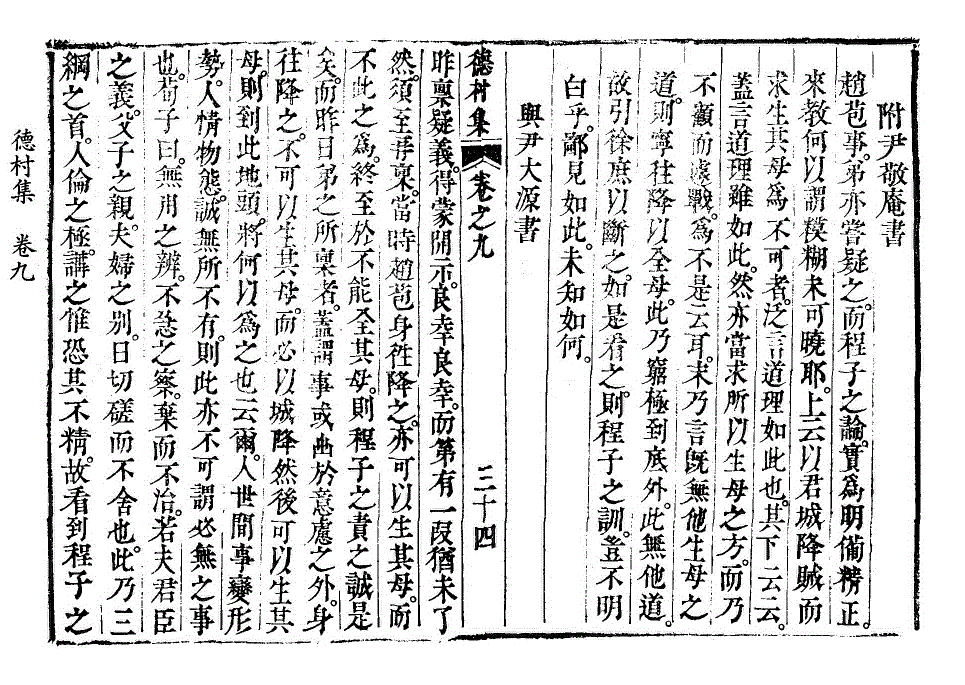 附尹敬庵书
附尹敬庵书赵苞事。弟亦尝疑之。而程子之论。实为明备精正。来教何以谓模糊未可晓耶。上云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为不可者。泛言道理如此也。其下云云。盖言道理虽如此。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而乃不顾而遽战。为不是云耳。末乃言既无他生母之道。则宁往降以全母。此乃穷极到底外。此无他道。故引徐庶以断之。如是看之。则程子之训。岂不明白乎。鄙见如此。未知如何。
与尹大源书
昨禀疑义。得蒙开示。良幸良幸。而第有一段犹未了然。须至再禀。当时赵苞身往降之。亦可以生其母。而不此之为。终至于不能全其母。则程子之责之诚是矣。而昨日弟之所禀者。盖谓事或出于意虑之外。身往降之。不可以生其母。而必以城降然后可以生其母。则到此地头。将何以为之也云尔。人世间事变形势。人情物态。诚无所不有。则此亦不可谓必无之事也。荀子曰。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日切磋而不舍也。此乃三纲之首。人伦之极。讲之惟恐其不精。故看到程子之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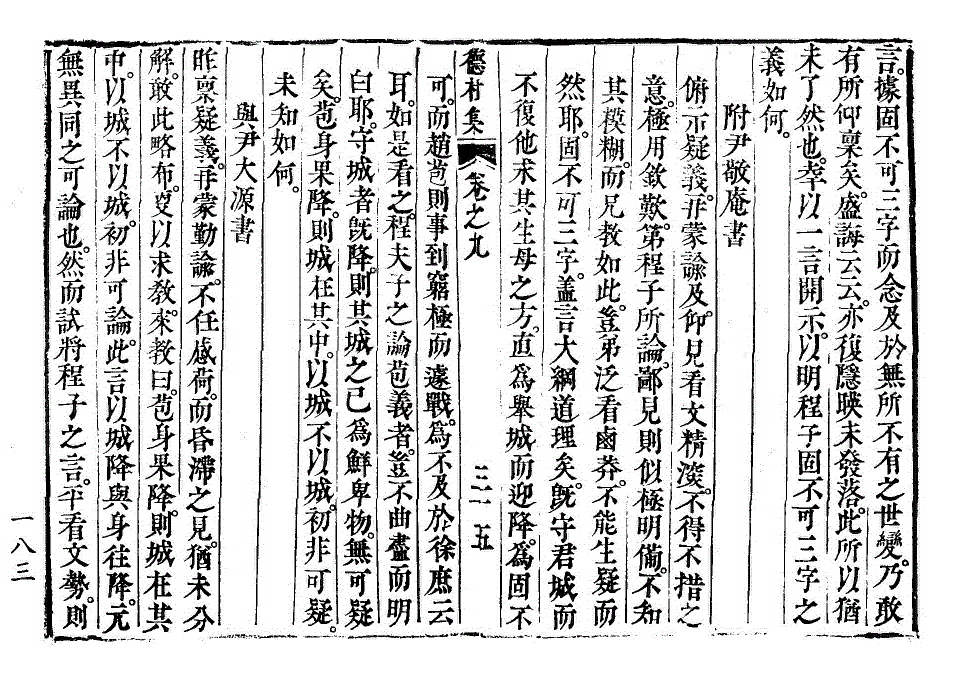 言。据固不可三字而念及于无所不有之世变。乃敢有所仰禀矣。盛诲云云。亦复隐映未发落。此所以犹未了然也。幸以一言开示。以明程子固不可三字之义如何。
言。据固不可三字而念及于无所不有之世变。乃敢有所仰禀矣。盛诲云云。亦复隐映未发落。此所以犹未了然也。幸以一言开示。以明程子固不可三字之义如何。附尹敬庵书
俯示疑义。再蒙谕及。仰见看文精深。不得不措之意。极用钦叹。第程子所论。鄙见则似极明备。不知其模糊。而兄教如此。岂弟泛看卤莽。不能生疑而然耶。固不可三字。盖言大纲道理矣。既守君城而不复他求其生母之方。直为举城而迎降。为固不可。而赵苞则事到穷极而遽战。为不及于徐庶云耳。如是看之。程夫子之论苞义者。岂不曲尽而明白耶。守城者既降。则其城之已为鲜卑物。无可疑矣。苞身果降。则城在其中。以城不以城。初非可疑。未知如何。
与尹大源书
昨禀疑义。再蒙勤谕。不任感荷。而昏滞之见。犹未分解。敢此略布。更以求教。来教曰。苞身果降。则城在其中。以城不以城。初非可论。此言以城降与身往降。元无异同之可论也。然而试将程子之言。平看文势。则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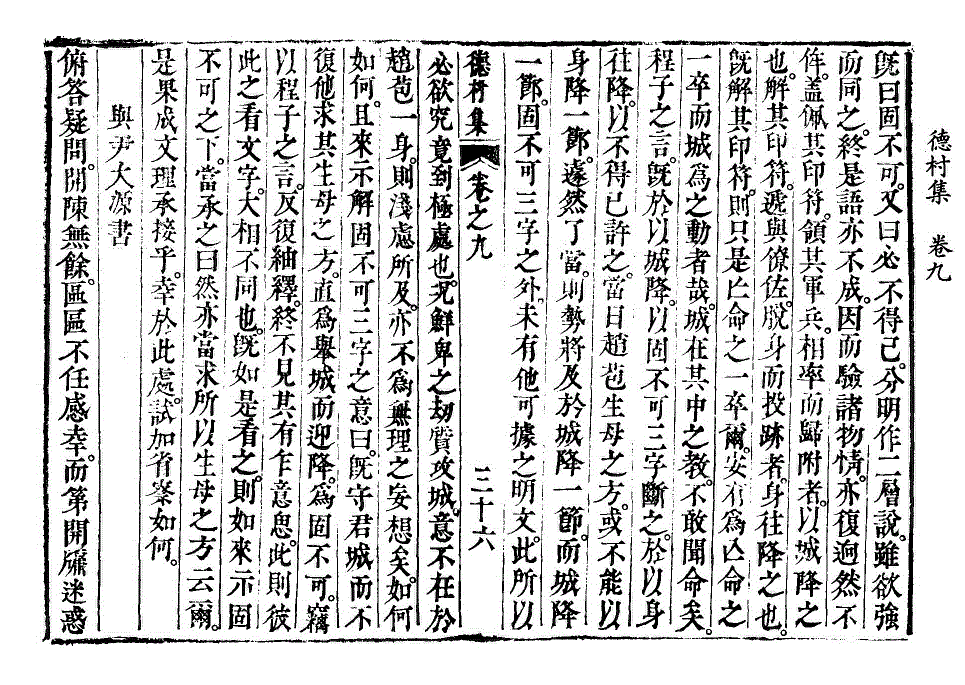 既曰固不可。又曰必不得已。分明作二层说。虽欲强而同之。终是语亦不成。因而验诸物情。亦复迥然不侔。盖佩其印符。领其军兵。相率而归附者。以城降之也。解其印符。递与僚佐。脱身而投迹者。身往降之也。既解其印符。则只是亡命之一卒尔。安有为亡命之一卒而城为之动者哉。城在其中之教。不敢闻命矣。程子之言。既于以城降。以固不可三字断之。于以身往降。以不得已许之。当日赵苞生母之方。或不能以身降一节。遽然了当。则势将及于城降一节。而城降一节。固不可三字之外。未有他可据之明文。此所以必欲究竟到极处也。况鲜卑之劫质攻城。意不在于赵苞一身。则浅虑所及。亦不为无理之妄想矣。如何如何。且来示解固不可三字之意曰。既守君城而不复他求其生母之方。直为举城而迎降。为固不可。窃以程子之言。反复䌷绎。终不见其有乍意思。此则彼此之看文字。大相不同也。既如是看之。则如来示固不可之下。当承之曰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云尔。是果成文理承接乎。幸于此处。试加省察如何。
既曰固不可。又曰必不得已。分明作二层说。虽欲强而同之。终是语亦不成。因而验诸物情。亦复迥然不侔。盖佩其印符。领其军兵。相率而归附者。以城降之也。解其印符。递与僚佐。脱身而投迹者。身往降之也。既解其印符。则只是亡命之一卒尔。安有为亡命之一卒而城为之动者哉。城在其中之教。不敢闻命矣。程子之言。既于以城降。以固不可三字断之。于以身往降。以不得已许之。当日赵苞生母之方。或不能以身降一节。遽然了当。则势将及于城降一节。而城降一节。固不可三字之外。未有他可据之明文。此所以必欲究竟到极处也。况鲜卑之劫质攻城。意不在于赵苞一身。则浅虑所及。亦不为无理之妄想矣。如何如何。且来示解固不可三字之意曰。既守君城而不复他求其生母之方。直为举城而迎降。为固不可。窃以程子之言。反复䌷绎。终不见其有乍意思。此则彼此之看文字。大相不同也。既如是看之。则如来示固不可之下。当承之曰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云尔。是果成文理承接乎。幸于此处。试加省察如何。与尹大源书
俯答疑问。开陈无馀。区区不任感幸。而第开牖迷惑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4L 页
 及究理精深之谕。窃不胜愧悚之私。大抵议论归一之前。彼此方持两端。各是其是。专务发明己意之所主。则必须先明彼说之不然。然后可以明吾说之不得不然。惟当各尽其说以要其归而已。不宜遽存形迹于其间也。抑弟之言语拙讷。文辞质俚。无复委曲回护之意。宜亦在所矜察。如何如何。噫。朱子曰。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此乃伦纲之一本处。义理之筑底处。讲之不厌其精。而未及解惑之前。不容蓄疑而含默。请复陈其说而明者择焉。夫既于以城降。以固不可三字断之。而至于必不得已然后方许身往降之。则其在语势事理。不得不以落二层观之矣。如来教所谓变而他求之云。有若或如此或如彼。无甚层分者。而亦必曰不得已云。则是至于穷极到底而不得。故变而他求也。亦非落二层而何耶。以城降与以身降。果若是无别。则一降字足矣。何必更藉城身二个剩字耶。亦何必分城字于固不可之前。身字于必不得已之后。浪费无用之辞说耶。且凡可不可之判。必挨到不得已之尽头。然后方可决其无憾于心。今者他求其生母之方而不得。然后许其以城降。则即是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为可矣。如之何其
及究理精深之谕。窃不胜愧悚之私。大抵议论归一之前。彼此方持两端。各是其是。专务发明己意之所主。则必须先明彼说之不然。然后可以明吾说之不得不然。惟当各尽其说以要其归而已。不宜遽存形迹于其间也。抑弟之言语拙讷。文辞质俚。无复委曲回护之意。宜亦在所矜察。如何如何。噫。朱子曰。物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此乃伦纲之一本处。义理之筑底处。讲之不厌其精。而未及解惑之前。不容蓄疑而含默。请复陈其说而明者择焉。夫既于以城降。以固不可三字断之。而至于必不得已然后方许身往降之。则其在语势事理。不得不以落二层观之矣。如来教所谓变而他求之云。有若或如此或如彼。无甚层分者。而亦必曰不得已云。则是至于穷极到底而不得。故变而他求也。亦非落二层而何耶。以城降与以身降。果若是无别。则一降字足矣。何必更藉城身二个剩字耶。亦何必分城字于固不可之前。身字于必不得已之后。浪费无用之辞说耶。且凡可不可之判。必挨到不得已之尽头。然后方可决其无憾于心。今者他求其生母之方而不得。然后许其以城降。则即是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为可矣。如之何其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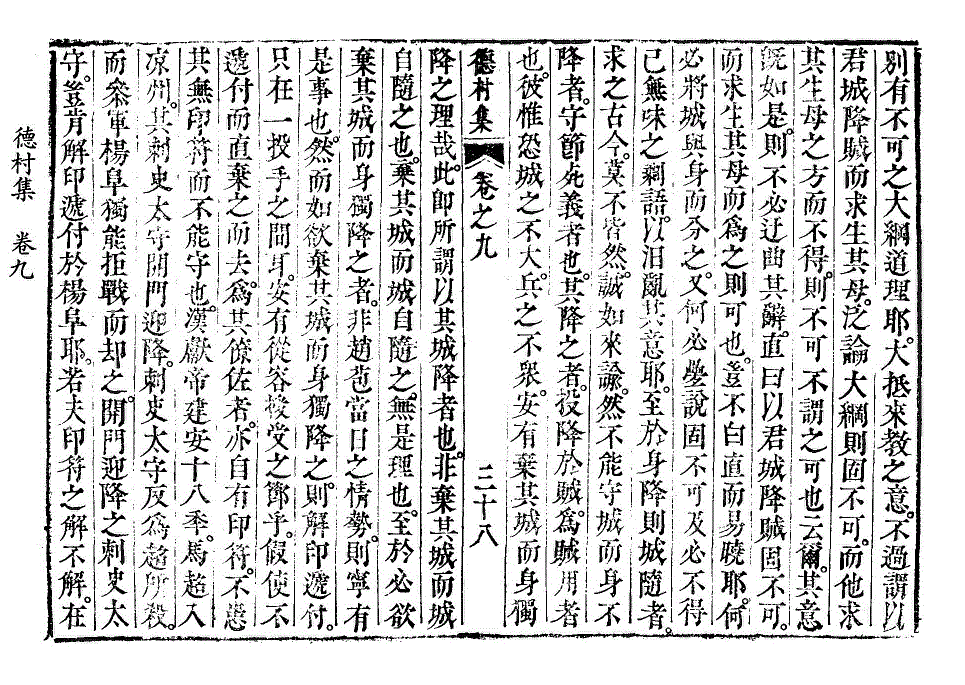 别有不可之大纲道理耶。大抵来教之意。不过谓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泛论大纲则固不可。而他求其生母之方而不得。则不可不谓之可也云尔。其意既如是。则不必迂曲其辞。直曰以君城降贼固不可。而求生其母而为之则可也。岂不白直而易晓耶。何必将城与身而分之。又何必叠说固不可及必不得已无味之剩语。以汩乱其意耶。至于身降则城随者。求之古今。莫不皆然。诚如来谕。然不能守城而身不降者。守节死义者也。其降之者。投降于贼。为贼用者也。彼惟恐城之不大。兵之不众。安有弃其城而身独降之理哉。此即所谓以其城降者也。非弃其城而城自随之也。弃其城而城自随之。无是理也。至于必欲弃其城而身独降之者。非赵苞当日之情势。则宁有是事也。然而如欲弃其城而身独降之。则解印递付。只在一投手之间耳。安有从容授受之节乎。假使不递付而直弃之而去。为其僚佐者。亦自有印符。不患其无印符而不能守也。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马超入凉州。其刺史太守开门迎降。刺史太守反为超所杀。而参军杨阜独能拒战而却之。开门迎降之刺史太守。岂肯解印递付于杨阜耶。若夫印符之解不解。在
别有不可之大纲道理耶。大抵来教之意。不过谓以君城降贼而求生其母。泛论大纲则固不可。而他求其生母之方而不得。则不可不谓之可也云尔。其意既如是。则不必迂曲其辞。直曰以君城降贼固不可。而求生其母而为之则可也。岂不白直而易晓耶。何必将城与身而分之。又何必叠说固不可及必不得已无味之剩语。以汩乱其意耶。至于身降则城随者。求之古今。莫不皆然。诚如来谕。然不能守城而身不降者。守节死义者也。其降之者。投降于贼。为贼用者也。彼惟恐城之不大。兵之不众。安有弃其城而身独降之理哉。此即所谓以其城降者也。非弃其城而城自随之也。弃其城而城自随之。无是理也。至于必欲弃其城而身独降之者。非赵苞当日之情势。则宁有是事也。然而如欲弃其城而身独降之。则解印递付。只在一投手之间耳。安有从容授受之节乎。假使不递付而直弃之而去。为其僚佐者。亦自有印符。不患其无印符而不能守也。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马超入凉州。其刺史太守开门迎降。刺史太守反为超所杀。而参军杨阜独能拒战而却之。开门迎降之刺史太守。岂肯解印递付于杨阜耶。若夫印符之解不解。在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5L 页
 我而已。非人所与。而既解其印符。则城自落空。不言可知。昨书所引耳馀之事。欲明此意而已。来书所明苞既解印递付而降。则城非苞有云者。非指此也耶。来书鲜卑虽劫质。而苞实无如之何云云以下。亦诚如所谕。但鲜卑之攻辽西。非为捕得赵苞。若使当初对阵出母示苞之时。谓之曰。吾之劫汝母。非为汝一身。汝今不以城降而以身来者。吾不活汝母云。则将若之何耶。昨书所谓万分有一云云。即此意也。程子之言。极于身降一节。而浅虑所及。尚有此不尽馀地。故必欲究竟到极处也。然而到今则烦渎甚矣。心甚不安。而愤悱之极。不能自已。特垂恕谅而终有以诲之。幸甚。寂居无聊。无可晤语。心有所怀。试为叩之。意固切于禀疑。而迹实涉于务胜。过此当置之耳。不宣。
我而已。非人所与。而既解其印符。则城自落空。不言可知。昨书所引耳馀之事。欲明此意而已。来书所明苞既解印递付而降。则城非苞有云者。非指此也耶。来书鲜卑虽劫质。而苞实无如之何云云以下。亦诚如所谕。但鲜卑之攻辽西。非为捕得赵苞。若使当初对阵出母示苞之时。谓之曰。吾之劫汝母。非为汝一身。汝今不以城降而以身来者。吾不活汝母云。则将若之何耶。昨书所谓万分有一云云。即此意也。程子之言。极于身降一节。而浅虑所及。尚有此不尽馀地。故必欲究竟到极处也。然而到今则烦渎甚矣。心甚不安。而愤悱之极。不能自已。特垂恕谅而终有以诲之。幸甚。寂居无聊。无可晤语。心有所怀。试为叩之。意固切于禀疑。而迹实涉于务胜。过此当置之耳。不宣。与尹大源书(戊午)
云云。纲目司马温公论嵇绍之事晋武帝曰。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嵇绍之于司马氏。乃不共天之雠也。效死于不共天之雠家。何以为君子之所许乎。蒙窃未晓。幸为示破如何。
附尹敬庵书
云云。温公之论嵇绍事。弟亦疑之。山公之劝绍事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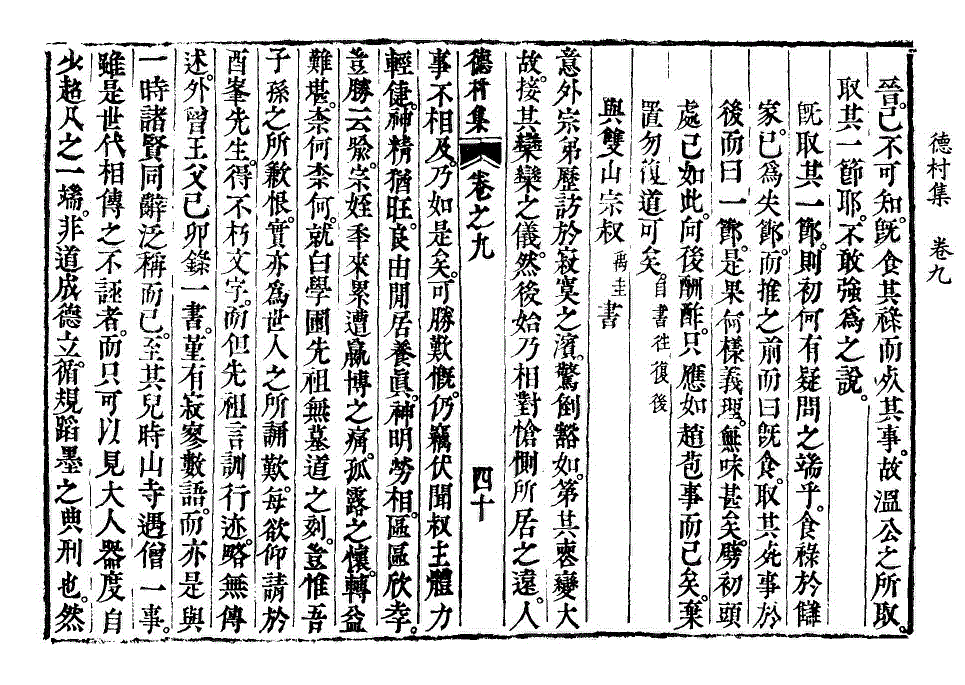 晋。已不可知。既食其禄而死其事。故温公之所取。取其一节耶。不敢强为之说。
晋。已不可知。既食其禄而死其事。故温公之所取。取其一节耶。不敢强为之说。既取其一节。则初何有疑问之端乎。食禄于雠家。已为失节。而推之前而曰既食。取其死事于后而曰一节。是果何样义理。无味甚矣。劈初头处已如此。向后酬酢。只应如赵苞事而已矣。弃置勿复道可矣。(自书往复后)
与双山宗叔(禹圭)书
意外宗弟历访于寂寞之滨。惊倒豁如。第其丧变大故。接其栾栾之仪。然后始乃相对怆恻所居之远。人事不相及。乃如是矣。可胜叹慨。仍窃伏闻叔主体力轻倢。神精犹旺。良由閒居养真。神明劳相。区区欣幸。岂胜云喻。宗侄年来累遭嬴博之痛。孤露之怀。转益难堪。柰何柰何。就白学圃先祖无墓道之刻。岂惟吾子孙之所歉恨。实亦为世人之所诵叹。每欲仰请于酉峰先生。得不朽文字。而但先祖言训行迹。略无传述。外曾王父己卯录一书。堇有寂寥数语。而亦是与一时诸贤同辞泛称而已。至其儿时山寺遇僧一事。虽是世代相传之不诬者。而只可以见大人器度自少超凡之一端。非道成德立。循规蹈墨之典刑也。然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6L 页
 则状德之文。何所凭依而说出数行语。搆成首尾关锁耶。然而此则实无柰兵燹之馀。文献无徵。区区浅虑。窃以为先祖之与静庵诸先生。虽以官职之高下。有被祸之轻重。而其讲学同业。补衮同心。进退同道。至今妇孺无不传诵。若得长者就此一款。据实直书。则自足为不朽之实矣。其他言行昧昧无传之故。则昔侍先人。细说先故。有闻以为先祖时文籍。并聚松川家。松川家没于兵难船避。故片言只字。无一得脱。夫以当时东莱松川兄弟文章交友之盛。亦必有请得状草于当世大手。而此亦无由考徵。诚可痛恨云云。此吾先祖言行之所以无传于后也。浅虑亦以为此一款。亦据实直书。使后世明知其所以无传之故。则犹胜于并与其所以无传之故而不传也。而传其所以不传。乃所以传也。松川家船陷事迹。朴山旋门文字。必有可考。而宗侄尚未得见景升兄弟。无由相逢叩问。伏想叔主家应有此等文字。伏望检考此事首尾。令侍人无遗誊书。而须致谨于船陷地方及年月等处。毋使少有差误。以之因便附送如何。明春南中科儒会行。应有历谒酉峰者。因此附送。则可无浮沉。书中亦有说不到处。细与宗弟讲讨。伏望俯询。幸
则状德之文。何所凭依而说出数行语。搆成首尾关锁耶。然而此则实无柰兵燹之馀。文献无徵。区区浅虑。窃以为先祖之与静庵诸先生。虽以官职之高下。有被祸之轻重。而其讲学同业。补衮同心。进退同道。至今妇孺无不传诵。若得长者就此一款。据实直书。则自足为不朽之实矣。其他言行昧昧无传之故。则昔侍先人。细说先故。有闻以为先祖时文籍。并聚松川家。松川家没于兵难船避。故片言只字。无一得脱。夫以当时东莱松川兄弟文章交友之盛。亦必有请得状草于当世大手。而此亦无由考徵。诚可痛恨云云。此吾先祖言行之所以无传于后也。浅虑亦以为此一款。亦据实直书。使后世明知其所以无传之故。则犹胜于并与其所以无传之故而不传也。而传其所以不传。乃所以传也。松川家船陷事迹。朴山旋门文字。必有可考。而宗侄尚未得见景升兄弟。无由相逢叩问。伏想叔主家应有此等文字。伏望检考此事首尾。令侍人无遗誊书。而须致谨于船陷地方及年月等处。毋使少有差误。以之因便附送如何。明春南中科儒会行。应有历谒酉峰者。因此附送。则可无浮沉。书中亦有说不到处。细与宗弟讲讨。伏望俯询。幸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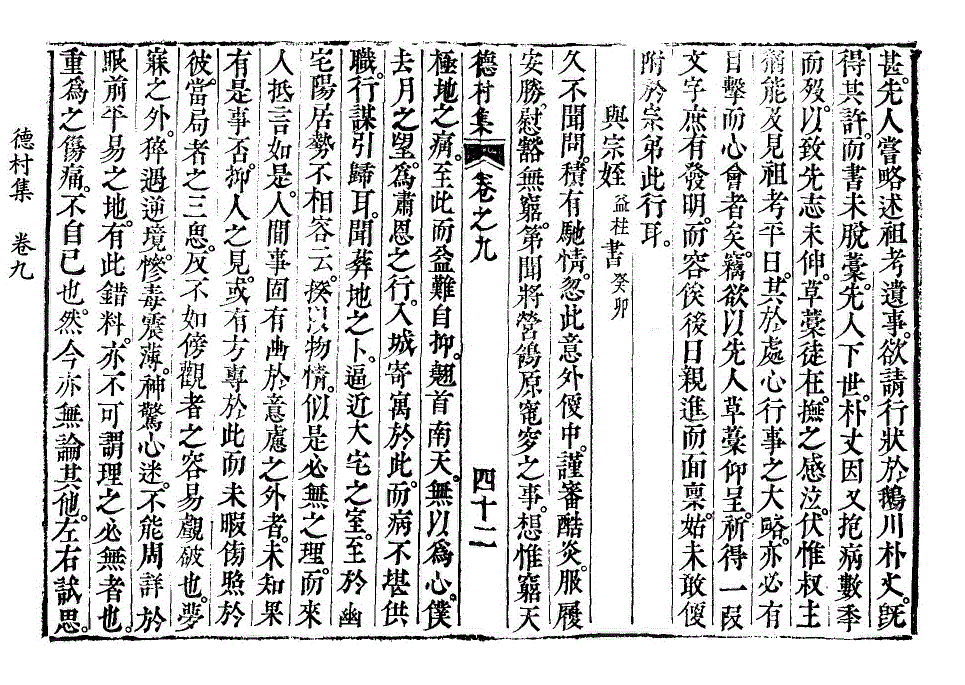 甚。先人尝略述祖考遗事。欲请行状于鹅川朴丈。既得其许。而书未脱稿。先人下世。朴丈因又抱病数年而殁。以致先志未伸。草稿徒在。抚之感泣。伏惟叔主犹能及见祖考平日。其于处心行事之大略。亦必有目击而心会者矣。窃欲以先人草藁仰呈。祈得一段文字庶有发明。而容俟后日亲进而面禀。姑未敢便附于宗弟此行耳。
甚。先人尝略述祖考遗事。欲请行状于鹅川朴丈。既得其许。而书未脱稿。先人下世。朴丈因又抱病数年而殁。以致先志未伸。草稿徒在。抚之感泣。伏惟叔主犹能及见祖考平日。其于处心行事之大略。亦必有目击而心会者矣。窃欲以先人草藁仰呈。祈得一段文字庶有发明。而容俟后日亲进而面禀。姑未敢便附于宗弟此行耳。与宗侄(益柱)书(癸卯)
久不闻问。积有驰情。忽此意外便中。谨审酷炎。服履安胜。慰豁无穷。第闻将营鸰原窀穸之事。想惟穷天极地之痛。至此而益难自抑。翘首南天。无以为心。仆去月之望。为肃恩之行。入城寄寓于此。而病不堪供职。行谋引归耳。闻葬地之卜。逼近大宅之室。至于幽宅阳居势不相容云。揆以物情。似是必无之理。而来人抵言如是。人间事固有出于意虑之外者。未知果有是事否。抑人之见。或有方专于此而未暇傍照于彼。当局者之三思。反不如傍观者之容易觑破也。梦寐之外。猝遇逆境。惨毒震薄。神惊心迷。不能周详于眼前平易之地。有此错料。亦不可谓理之必无者也。重为之伤痛。不自已也。然今亦无论其他。左右试思。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7L 页
 此个基宅。为何等重且大耶。四世庙主之所安奉。而尊季母夫人之所日夕兴寝之地。则求诸神道人情。岂容如是耶。固知因一时商确之际。偶尔言端之及。岂容无传闻之爽实。而既有所闻。不能无过虑之忧。不敢不以相悉。幸惟谅之。到今则左右身上。尽有一重担负。与曩时自别。而此系一门内事。吾亦不可恝然越视。则凡有所怀。不以布于左右而更于何地耶。千万谅之。
此个基宅。为何等重且大耶。四世庙主之所安奉。而尊季母夫人之所日夕兴寝之地。则求诸神道人情。岂容如是耶。固知因一时商确之际。偶尔言端之及。岂容无传闻之爽实。而既有所闻。不能无过虑之忧。不敢不以相悉。幸惟谅之。到今则左右身上。尽有一重担负。与曩时自别。而此系一门内事。吾亦不可恝然越视。则凡有所怀。不以布于左右而更于何地耶。千万谅之。与从兄(处中)书(丙戌)
自春徂秋。音信杳然。悠悠瞻慕。何日少弛。未审即日。伯母主气候平安。佥兄主閤内诸况。各得安稳否。弟于七月廿一日政。得除怀仁。八月十六日肃𧬄。已于去月十五。奉板舆到邑。亲候平安。儿辈亦各好在。幸不可言。邑虽残薄。而奉亲一节。比之在家。不啻相胜。此外何望。静夫陪行同来。留十数日。为其看检家事。方又下去。而欲及老亲生辰时上来。佥兄主及诸从弟中数员与直卿联辔而来。因与过岁于此。明春弟之省墓之行。又与之同下则似好矣。未知如何。非但弟之孤寂为可闷。老亲生辰。诸从兄弟团聚献觞。则其于慰悦老人之心。为如何哉。望须毋以路远为难。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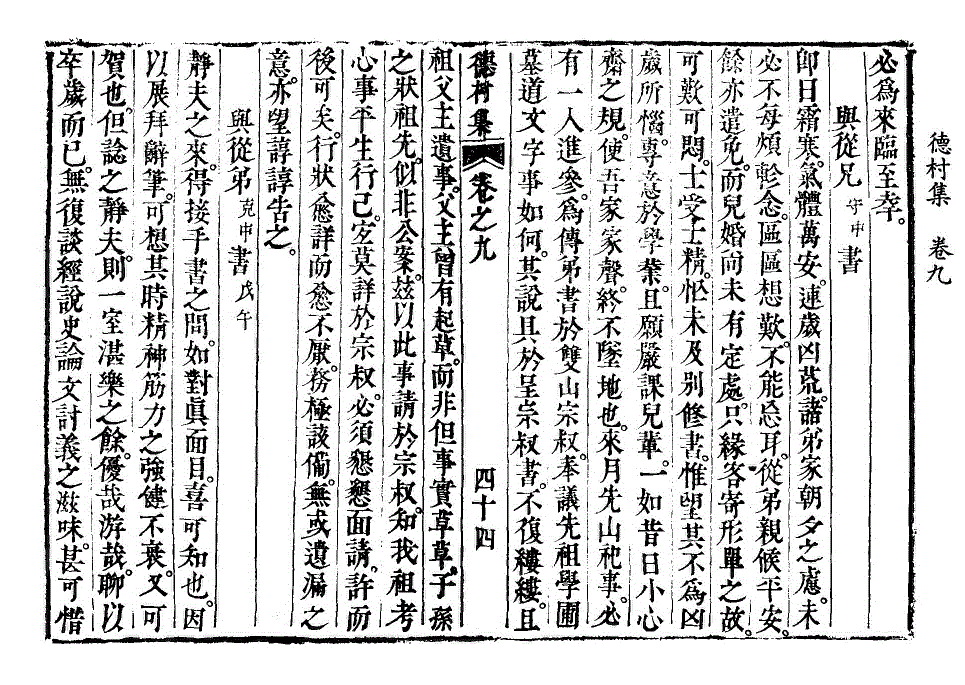 必为来临至幸。
必为来临至幸。与从兄(守中)书
即日霜寒。气体万安。连岁凶荒。诸弟家朝夕之虑。未必不每烦轸念。区区想叹。不能忘耳。从弟亲候平安。馀亦遣免。而儿婚尚未有定处。只缘客寄形单之故。可叹可闷。士受,士精。忙未及别修书。惟望其不为凶岁所恼。专意于学业。且愿严课儿辈。一如昔日小心斋之规。使吾家家声。终不坠地也。来月先山祀事。必有一人进参。为传弟书于双山宗叔。奉议先祖学圃墓道文字事如何。其说具于呈宗叔书。不复缕缕。且祖父主遗事。父主曾有起草。而非但事实草草。子孙之状祖先。似非公案。玆以此事请于宗叔。知我祖考心事平生行己。宜莫详于宗叔。必须恳恳面请。许而后可矣。行状愈详而愈不厌。务极该备。无或遗漏之意。亦望谆谆告之。
与从弟(克中)书(戊午)
静夫之来。得接手书之问。如对真面目。喜可知也。因以展拜辞笔。可想其时精神筋力之强健不衰。又可贺也。但谂之静夫。则一室湛乐之馀。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无复谈经说史论文讨义之滋味。甚可惜
德村先生集卷之九 第 188L 页
 也。士生此世。纵不能立身扬名。岂肯甘自枯落。泯泯没没。奄过百年乎。吾于此中。有数件文字讲论经史。而左右森立。无非褰裳于党论。无可开喙。唯与儿子辈时时相对说及而已。明秋南下。准拟与君剧论。以续少日小心斋旧业。君须从今为始痛改旧习。日以经籍自娱。使吾相对。刮目如何。
也。士生此世。纵不能立身扬名。岂肯甘自枯落。泯泯没没。奄过百年乎。吾于此中。有数件文字讲论经史。而左右森立。无非褰裳于党论。无可开喙。唯与儿子辈时时相对说及而已。明秋南下。准拟与君剧论。以续少日小心斋旧业。君须从今为始痛改旧习。日以经籍自娱。使吾相对。刮目如何。与尹厦卿(光厦)书(先生孙婿。庚申正月初四日。)
新元侍奉万福。此中廑支如昨耳。孙女解娩无事而得弄璋之喜耶。儿子方读书于书室。君未可来与同案以做数月之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