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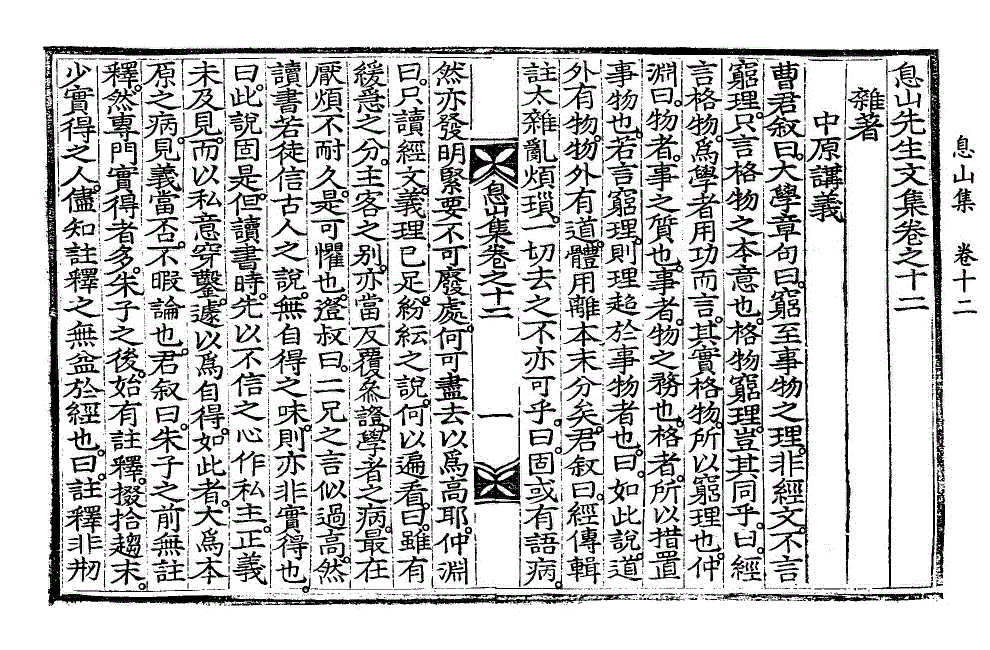 中原讲义
中原讲义曹君叙曰。大学章句曰。穷至事物之理。非经文。不言穷理。只言格物之本意也。格物穷理。岂其同乎。曰。经言格物。为学者用功而言。其实格物。所以穷理也。仲渊曰。物者。事之质也。事者。物之务也。格者。所以措置事物也。若言穷理。则理超于事物者也。曰。如此说。道外有物。物外有道。体用离本末分矣。君叙曰。经传辑注太杂乱烦琐。一切去之不亦可乎。曰。固或有语病。然亦发明紧要不可废处。何可尽去以为高耶。仲渊曰。只读经文。义理已足。纷纭之说。何以遍看。曰。虽有缓急之分。主客之别。亦当反覆参證。学者之病。最在厌烦不耐久。是可惧也。澄叔曰。二兄之言似过高。然读书若徒信古人之说。无自得之味。则亦非实得也。曰。此说固是。但读书时。先以不信之心作私主。正义未及见。而以私意穿凿。遽以为自得。如此者。大为本原之病。见义当否。不暇论也。君叙曰。朱子之前无注释。然专门实得者多。朱子之后。始有注释。掇拾趋末。少实得之人。尽知注释之无益于经也。曰。注释非刱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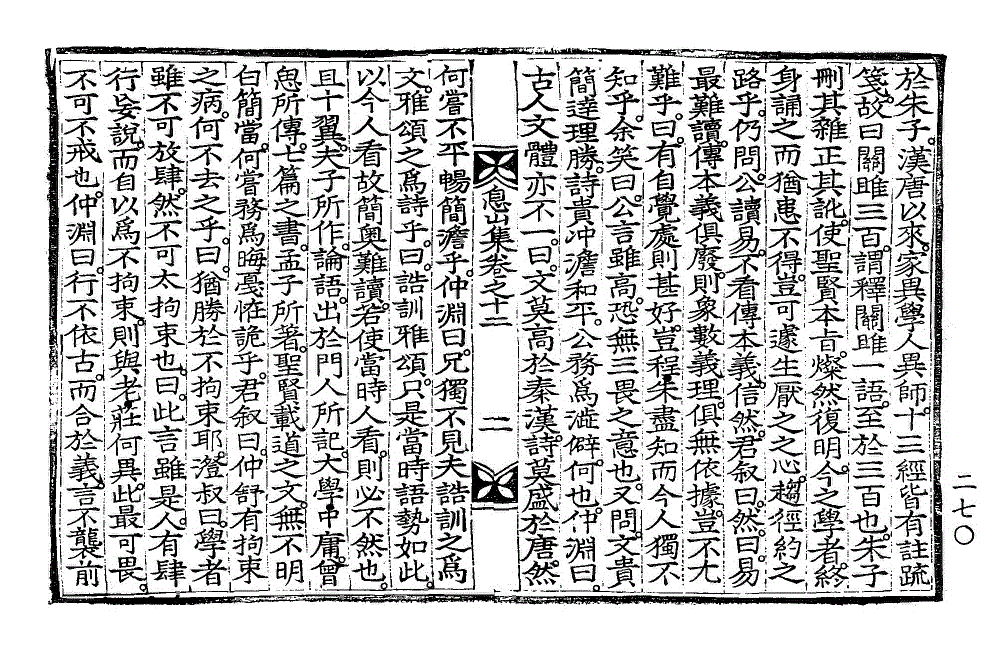 于朱子。汉唐以来。家异学人异师。十三经皆有注疏笺。故曰关雎三百。谓释关雎一语。至于三百也。朱子删其杂正其讹。使圣贤本旨。灿然复明。今之学者。终身诵之而犹患不得。岂可遽生厌之之心。趋径约之路乎。仍问。公读易。不看传本义。信然。君叙曰。然。曰。易最难读。传本义俱废。则象数义理。俱无依据。岂不尤难乎。曰。有自觉处则甚好。岂程,朱尽知而今人独不知乎。余笑曰。公言虽高。恐无三畏之意也。又问。文贵简达理胜。诗贵冲澹和平。公务为涩僻。何也。仲渊曰。古人文体亦不一。曰。文莫高于秦汉。诗莫盛于唐。然何尝不平畅简澹乎。仲渊曰。兄独不见夫诰训之为文。雅颂之为诗乎。曰。诰训雅颂。只是当时语势如此。以今人看故简奥难读。若使当时人看。则必不然也。且十翼。夫子所作。论语。出于门人所记。大学,中庸。曾,思所传。七篇之书。孟子所著。圣贤载道之文。无不明白简当。何尝务为晦戛怪诡乎。君叙曰。仲舒有拘束之病。何不去之乎。曰。犹胜于不拘束耶。澄叔曰。学者虽不可放肆。然不可太拘束也。曰。此言虽是。人有肆行妄说。而自以为不拘束。则与老,庄何异。此最可畏。不可不戒也。仲渊曰。行不依古。而合于义。言不袭前
于朱子。汉唐以来。家异学人异师。十三经皆有注疏笺。故曰关雎三百。谓释关雎一语。至于三百也。朱子删其杂正其讹。使圣贤本旨。灿然复明。今之学者。终身诵之而犹患不得。岂可遽生厌之之心。趋径约之路乎。仍问。公读易。不看传本义。信然。君叙曰。然。曰。易最难读。传本义俱废。则象数义理。俱无依据。岂不尤难乎。曰。有自觉处则甚好。岂程,朱尽知而今人独不知乎。余笑曰。公言虽高。恐无三畏之意也。又问。文贵简达理胜。诗贵冲澹和平。公务为涩僻。何也。仲渊曰。古人文体亦不一。曰。文莫高于秦汉。诗莫盛于唐。然何尝不平畅简澹乎。仲渊曰。兄独不见夫诰训之为文。雅颂之为诗乎。曰。诰训雅颂。只是当时语势如此。以今人看故简奥难读。若使当时人看。则必不然也。且十翼。夫子所作。论语。出于门人所记。大学,中庸。曾,思所传。七篇之书。孟子所著。圣贤载道之文。无不明白简当。何尝务为晦戛怪诡乎。君叙曰。仲舒有拘束之病。何不去之乎。曰。犹胜于不拘束耶。澄叔曰。学者虽不可放肆。然不可太拘束也。曰。此言虽是。人有肆行妄说。而自以为不拘束。则与老,庄何异。此最可畏。不可不戒也。仲渊曰。行不依古。而合于义。言不袭前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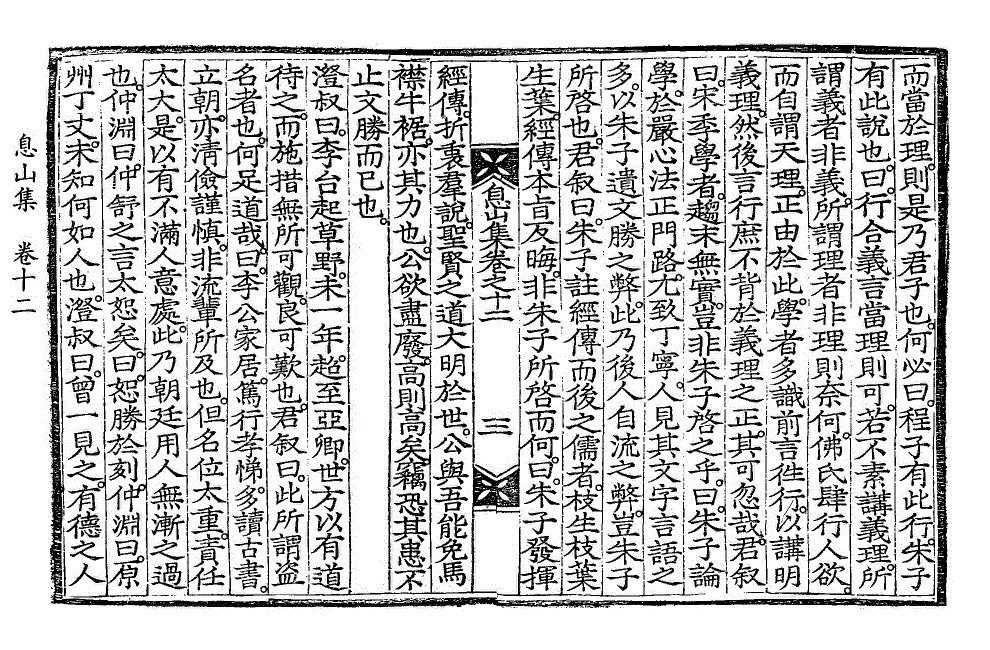 而当于理。则是乃君子也。何必曰。程子有此行。朱子有此说也。曰。行合义言当理则可。若不素讲义理。所谓义者非义。所谓理者非理则奈何。佛氏肆行人欲。而自谓天理。正由于此。学者多识前言往行。以讲明义理。然后言行庶不背于义理之正。其可忽哉。君叙曰。宋季学者。趋末无实。岂非朱子启之乎。曰。朱子论学。于严心法正门路。尤致丁宁。人见其文字言语之多。以朱子遗文胜之弊。此乃后人自流之弊。岂朱子所启也。君叙曰。朱子注经传而后之儒者。枝生枝叶生叶。经传本旨反晦。非朱子所启而何。曰。朱子发挥经传。折衷群说。圣贤之道大明于世。公与吾能免马襟牛裾。亦其力也。公欲尽废。高则高矣。窃恐其患不止文胜而已也。
而当于理。则是乃君子也。何必曰。程子有此行。朱子有此说也。曰。行合义言当理则可。若不素讲义理。所谓义者非义。所谓理者非理则奈何。佛氏肆行人欲。而自谓天理。正由于此。学者多识前言往行。以讲明义理。然后言行庶不背于义理之正。其可忽哉。君叙曰。宋季学者。趋末无实。岂非朱子启之乎。曰。朱子论学。于严心法正门路。尤致丁宁。人见其文字言语之多。以朱子遗文胜之弊。此乃后人自流之弊。岂朱子所启也。君叙曰。朱子注经传而后之儒者。枝生枝叶生叶。经传本旨反晦。非朱子所启而何。曰。朱子发挥经传。折衷群说。圣贤之道大明于世。公与吾能免马襟牛裾。亦其力也。公欲尽废。高则高矣。窃恐其患不止文胜而已也。澄叔曰。李台起草野。未一年。超至亚卿。世方以有道待之。而施措无所可观。良可叹也。君叙曰。此所谓盗名者也。何足道哉。曰。李公家居。笃行孝悌。多读古书。立朝。亦清俭谨慎。非流辈所及也。但名位太重。责任太大。是以有不满人意处。此乃朝廷用人无渐之过也。仲渊曰。仲舒之言太恕矣。曰。恕胜于刻。仲渊曰。原州丁丈。未知何如人也。澄叔曰。曾一见之。有德之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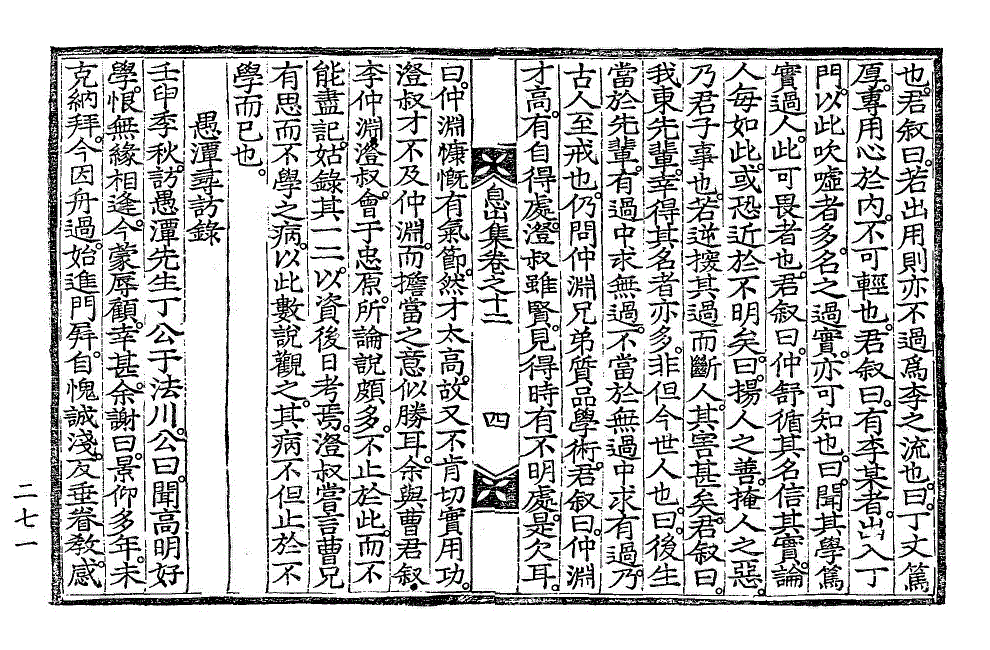 也。君叙曰。若出用则亦不过为李之流也。曰。丁丈笃厚。专用心于内。不可轻也。君叙曰。有李某者。出入丁门。以此吹嘘者多。名之过实。亦可知也。曰。闻其学笃实过人。此可畏者也。君叙曰。仲舒循其名信其实。论人每如此。或恐近于不明矣。曰。扬人之善。掩人之恶。乃君子事也。若逆探其过而断人。其害甚矣。君叙曰。我东先辈。幸得其名者亦多。非但今世人也。曰。后生当于先辈。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乃古人至戒也。仍问仲渊兄弟质品学术。君叙曰。仲渊才高。有自得处。澄叔虽贤。见得时有不明处。是欠耳。曰。仲渊慷慨有气节。然才太高。故又不肯切实用功。澄叔才不及仲渊。而担当之意似胜耳。余与曹君叙,李仲渊,澄叔。会于忠原。所论说颇多。不止于此。而不能尽记。姑录其一二。以资后日考焉。澄叔尝言曹兄有思而不学之病。以此数说观之。其病不但止于不学而已也。
也。君叙曰。若出用则亦不过为李之流也。曰。丁丈笃厚。专用心于内。不可轻也。君叙曰。有李某者。出入丁门。以此吹嘘者多。名之过实。亦可知也。曰。闻其学笃实过人。此可畏者也。君叙曰。仲舒循其名信其实。论人每如此。或恐近于不明矣。曰。扬人之善。掩人之恶。乃君子事也。若逆探其过而断人。其害甚矣。君叙曰。我东先辈。幸得其名者亦多。非但今世人也。曰。后生当于先辈。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乃古人至戒也。仍问仲渊兄弟质品学术。君叙曰。仲渊才高。有自得处。澄叔虽贤。见得时有不明处。是欠耳。曰。仲渊慷慨有气节。然才太高。故又不肯切实用功。澄叔才不及仲渊。而担当之意似胜耳。余与曹君叙,李仲渊,澄叔。会于忠原。所论说颇多。不止于此。而不能尽记。姑录其一二。以资后日考焉。澄叔尝言曹兄有思而不学之病。以此数说观之。其病不但止于不学而已也。愚潭寻访录
壬申季秋。访愚潭先生丁公于法川。公曰。闻高明好学。恨无缘相逢。今蒙辱顾。幸甚。余谢曰。景仰多年。未克纳拜。今因舟过。始进门屏。自愧诚浅。反垂眷教。感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2H 页
 拜不知所言也。磬折虽晚。一言辱教。是后生之愿也。公曰。某素钝劣。殊无所闻。何以答高明勤意。谦退不已。且曰。闻高明与李君溆为友讲磨。未知李君学术志业如何。对曰。李某与鄙家。世谊甚厚。自少亲爱其气宇磊落。好古向善。但缘博而少驳。若克治变化。其进不可量也。公曰。责善朋友之道。高明可以任之。对曰。李友志操。自是不泛。其病痛处。渠已自知。亦尝以鄙言为是耳。且闻李敬叔出入门下最久。笃行力践。为之钦叹。公曰。诚是不易得之人也。曰。自少学于先生乎。公曰。自少相从。然某之学于敬叔者多。岂敢教敬叔也。曰。敬叔见处与先生皆合乎。公曰。某无所见。敬叔博学多识。每相见时观感之益居多。此所以敬之也。讲论之事。某所不及。而亦何以少无差殊也。时汉阴碑文新出矣。公为诵其与赵,李两家书言曰。事实如此。无处㬥白。鄙人不孝之罪。将不容于覆载也。或谓鄙人亲入洛下。消详于两家子弟。以为变通之地。然自念此非正当道理。只陈其实状。尽在我者。而至于碑文之改否。不可必也。未知如何。对曰。所教极当。此事若不慎重。恐或起闹也。公曰。诚然诚然。仍语及山水。于是。公颇舒气扬声。历论诸名山大川。亹亹
拜不知所言也。磬折虽晚。一言辱教。是后生之愿也。公曰。某素钝劣。殊无所闻。何以答高明勤意。谦退不已。且曰。闻高明与李君溆为友讲磨。未知李君学术志业如何。对曰。李某与鄙家。世谊甚厚。自少亲爱其气宇磊落。好古向善。但缘博而少驳。若克治变化。其进不可量也。公曰。责善朋友之道。高明可以任之。对曰。李友志操。自是不泛。其病痛处。渠已自知。亦尝以鄙言为是耳。且闻李敬叔出入门下最久。笃行力践。为之钦叹。公曰。诚是不易得之人也。曰。自少学于先生乎。公曰。自少相从。然某之学于敬叔者多。岂敢教敬叔也。曰。敬叔见处与先生皆合乎。公曰。某无所见。敬叔博学多识。每相见时观感之益居多。此所以敬之也。讲论之事。某所不及。而亦何以少无差殊也。时汉阴碑文新出矣。公为诵其与赵,李两家书言曰。事实如此。无处㬥白。鄙人不孝之罪。将不容于覆载也。或谓鄙人亲入洛下。消详于两家子弟。以为变通之地。然自念此非正当道理。只陈其实状。尽在我者。而至于碑文之改否。不可必也。未知如何。对曰。所教极当。此事若不慎重。恐或起闹也。公曰。诚然诚然。仍语及山水。于是。公颇舒气扬声。历论诸名山大川。亹亹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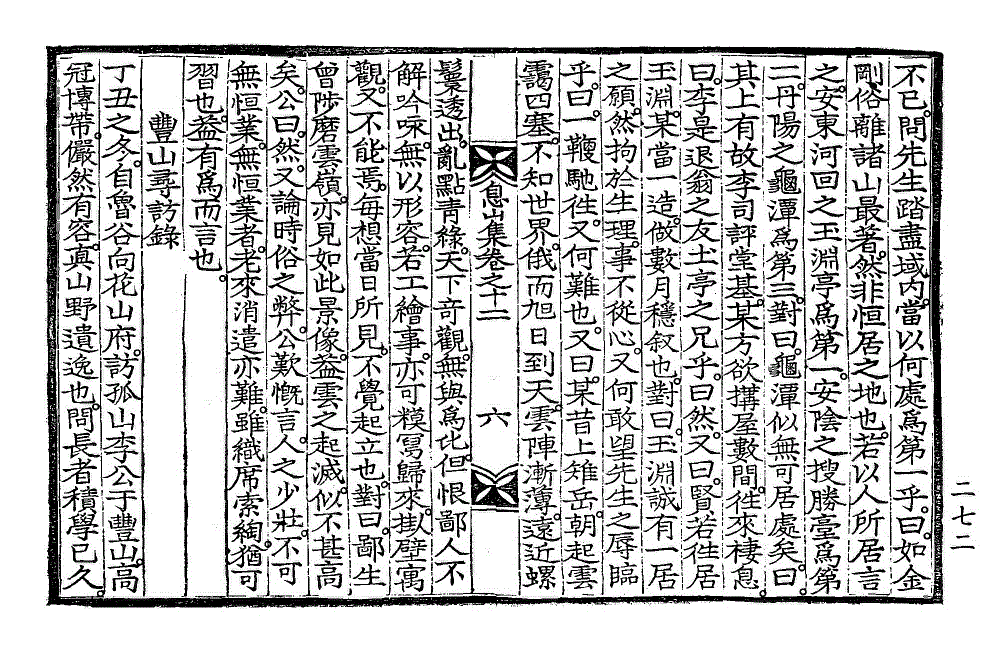 不已。问先生踏尽域内。当以何处为第一乎。曰。如金刚,俗离诸山最著。然非恒居之地也。若以人所居言之。安东河回之玉渊亭为第一。安阴之搜胜台为第二。丹阳之龟潭为第三。对曰。龟潭似无可居处矣。曰。其上有故李司评堂基。某方欲搆屋数间。往来栖息。曰。李是退翁之友土亭之兄乎。曰然。又曰。贤若往居玉渊。某当一造。做数月稳叙也。对曰。玉渊诚有一居之愿。然拘于生理。事不从心。又何敢望先生之辱临乎。曰。一鞭驰往。又何难也。又曰。某昔上雉岳。朝起云霭四塞。不知世界。俄而旭日到天。云阵渐薄。远近螺鬟透出。乱点青绿。天下奇观。无与为比。但恨鄙人不解吟咏。无以形容。若工绘事。亦可模写归来。挂壁寓观。又不能焉。每想当日所见。不觉起立也。对曰。鄙生曾陟磨云岭。亦见如此景像。盖云之起灭。似不甚高矣。公曰。然。又论时俗之弊。公叹慨言。人之少壮。不可无恒业。无恒业者。老来消遣亦难。虽织席索绹。犹可习也。盖有为而言也。
不已。问先生踏尽域内。当以何处为第一乎。曰。如金刚,俗离诸山最著。然非恒居之地也。若以人所居言之。安东河回之玉渊亭为第一。安阴之搜胜台为第二。丹阳之龟潭为第三。对曰。龟潭似无可居处矣。曰。其上有故李司评堂基。某方欲搆屋数间。往来栖息。曰。李是退翁之友土亭之兄乎。曰然。又曰。贤若往居玉渊。某当一造。做数月稳叙也。对曰。玉渊诚有一居之愿。然拘于生理。事不从心。又何敢望先生之辱临乎。曰。一鞭驰往。又何难也。又曰。某昔上雉岳。朝起云霭四塞。不知世界。俄而旭日到天。云阵渐薄。远近螺鬟透出。乱点青绿。天下奇观。无与为比。但恨鄙人不解吟咏。无以形容。若工绘事。亦可模写归来。挂壁寓观。又不能焉。每想当日所见。不觉起立也。对曰。鄙生曾陟磨云岭。亦见如此景像。盖云之起灭。似不甚高矣。公曰。然。又论时俗之弊。公叹慨言。人之少壮。不可无恒业。无恒业者。老来消遣亦难。虽织席索绹。犹可习也。盖有为而言也。丰山寻访录
丁丑之冬。自鲁谷向花山府。访孤山李公于丰山。高冠博带。俨然有容。真山野遗逸也。问长者积学已久。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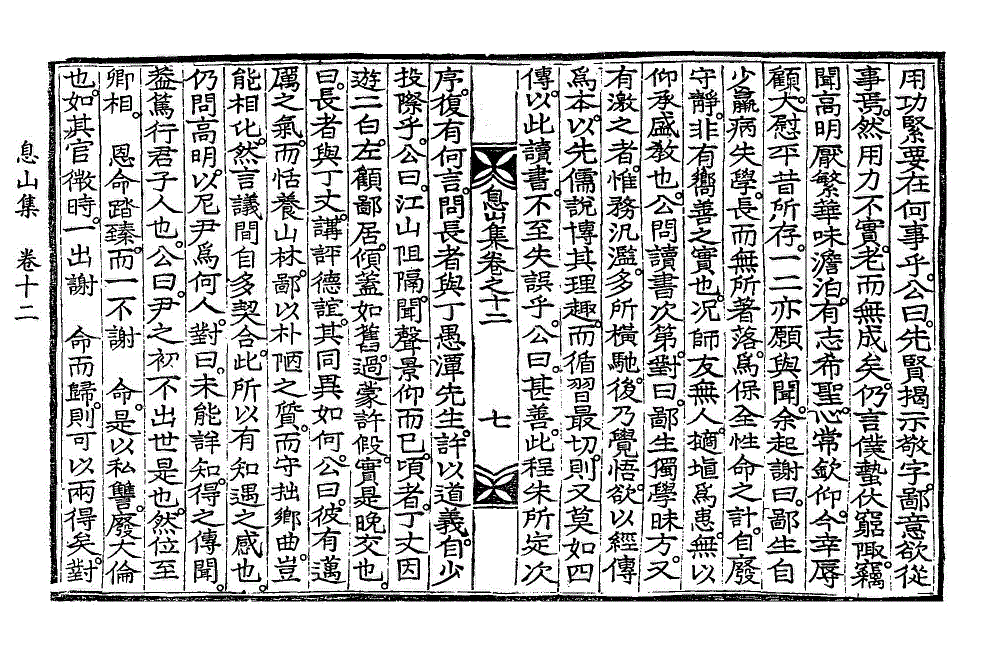 用功紧要在何事乎。公曰。先贤揭示敬字。鄙意欲从事焉。然用力不实。老而无成矣。仍言仆蛰伏穷陬。窃闻高明厌繁华味澹泊。有志希圣。心常钦仰。今幸辱顾。大慰平昔所存。一二亦愿与闻。余起谢曰。鄙生自少羸病失学。长而无所著落。为保全性命之计。自废守静。非有向善之实也。况师友无人。擿埴为患。无以仰承盛教也。公问读书次第。对曰。鄙生独学昧方。又有激之者。惟务汎滥。多所横驰。后乃觉悟。欲以经传为本。以先儒说博其理趣。而循习最切。则又莫如四传。以此读书。不至失误乎。公曰。甚善。此程朱所定次序。复有何言。问长者与丁愚潭先生。许以道义。自少投际乎。公曰。江山阻隔。闻声景仰而已。顷者。丁丈因游二白。左顾鄙居。倾盖如旧。过蒙许假。实是晚交也。曰。长者与丁丈。讲评德谊。其同异如何。公曰。彼有迈厉之气。而恬养山林。鄙以朴陋之质。而守拙乡曲。岂能相比。然言议间自多契合。此所以有知遇之感也。仍问高明。以尼尹为何人。对曰。未能详知。得之传闻。盖笃行君子人也。公曰。尹之初不出世是也。然位至卿相。 恩命踏臻。而一不谢 命。是以私雠。废大伦也。如其官微时。一出谢 命而归。则可以两得矣。对
用功紧要在何事乎。公曰。先贤揭示敬字。鄙意欲从事焉。然用力不实。老而无成矣。仍言仆蛰伏穷陬。窃闻高明厌繁华味澹泊。有志希圣。心常钦仰。今幸辱顾。大慰平昔所存。一二亦愿与闻。余起谢曰。鄙生自少羸病失学。长而无所著落。为保全性命之计。自废守静。非有向善之实也。况师友无人。擿埴为患。无以仰承盛教也。公问读书次第。对曰。鄙生独学昧方。又有激之者。惟务汎滥。多所横驰。后乃觉悟。欲以经传为本。以先儒说博其理趣。而循习最切。则又莫如四传。以此读书。不至失误乎。公曰。甚善。此程朱所定次序。复有何言。问长者与丁愚潭先生。许以道义。自少投际乎。公曰。江山阻隔。闻声景仰而已。顷者。丁丈因游二白。左顾鄙居。倾盖如旧。过蒙许假。实是晚交也。曰。长者与丁丈。讲评德谊。其同异如何。公曰。彼有迈厉之气。而恬养山林。鄙以朴陋之质。而守拙乡曲。岂能相比。然言议间自多契合。此所以有知遇之感也。仍问高明。以尼尹为何人。对曰。未能详知。得之传闻。盖笃行君子人也。公曰。尹之初不出世是也。然位至卿相。 恩命踏臻。而一不谢 命。是以私雠。废大伦也。如其官微时。一出谢 命而归。则可以两得矣。对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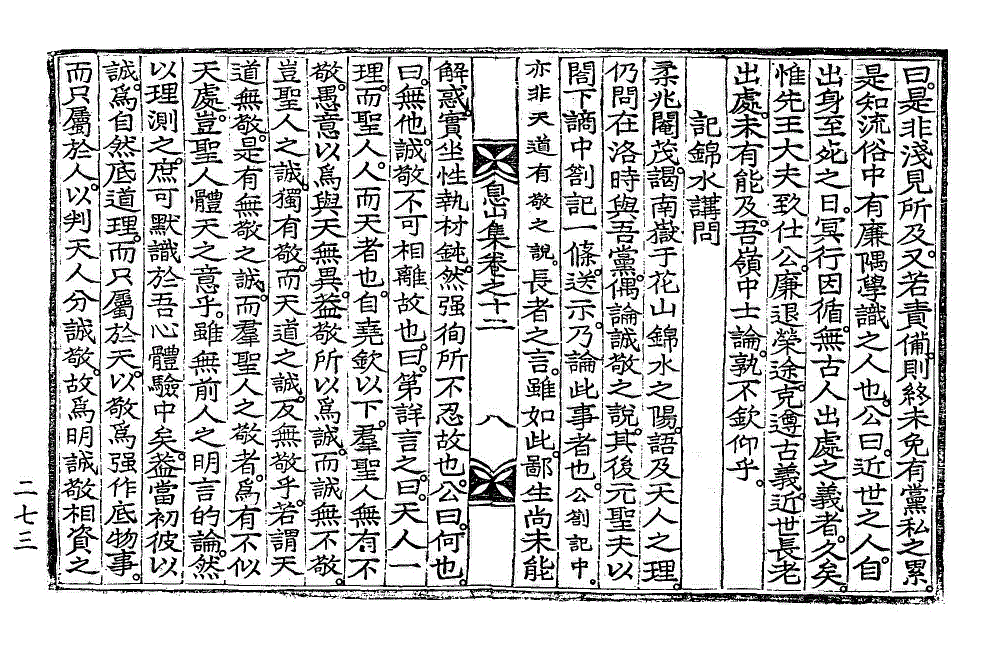 曰。是非浅见所及。又若责备。则终未免有党私之累。是知流俗中有廉隅学识之人也。公曰。近世之人。自出身至死之日。冥行因循。无古人出处之义者。久矣。惟先王大夫致仕公。廉退荣途。克遵古义。近世长老出处。未有能及。吾岭中士论。孰不钦仰乎。
曰。是非浅见所及。又若责备。则终未免有党私之累。是知流俗中有廉隅学识之人也。公曰。近世之人。自出身至死之日。冥行因循。无古人出处之义者。久矣。惟先王大夫致仕公。廉退荣途。克遵古义。近世长老出处。未有能及。吾岭中士论。孰不钦仰乎。记锦水讲问
柔兆阉茂。谒南岳于花山锦水之阳。语及天人之理。仍问在洛时与吾党。偶论诚敬之说。其后元圣夫以閤下谪中劄记一条。送示。乃论此事者也。(公劄记中。亦非天道有敬之说。)长者之言。虽如此。鄙生尚未能解惑。实坐性执材钝。然强徇所不忍故也。公曰。何也。曰。无他。诚敬不可相离故也。曰。第详言之。曰。天人一理。而圣人。人而天者也。自尧钦以下。群圣人无有不敬。愚意以为与天无异。盖敬所以为诚。而诚无不敬。岂圣人之诚。独有敬。而天道之诚。反无敬乎。若谓天道无敬。是有无敬之诚。而群圣人之敬者。为有不似天处。岂圣人体天之意乎。虽无前人之明言的论。然以理测之。庶可默识于吾心体验中矣。盖当初彼以诚。为自然底道理。而只属于天。以敬为强作底物事。而只属于人。以判天人分诚敬。故为明诚敬相资之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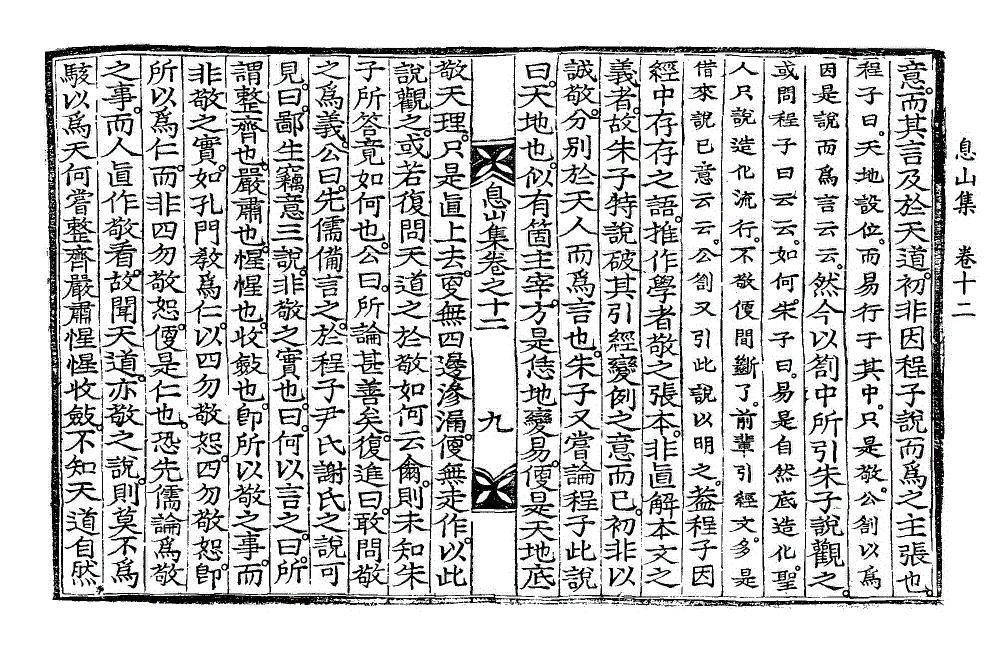 意。而其言及于天道。初非因程子说而为之主张也。(程子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于其中。只是敬。公劄以为因是说而为言云云。)然今以劄中所引朱子说观之。(或问程子曰云云。如何。朱子曰。易是自然底造化。圣人只说造化流行。不敬便间断了。前辈引经文。多是借来说己意云云。公劄又引此说以明之。)盖程子因经中存存之语。推作学者敬之张本。非直解本文之义者。故朱子特说破其引经变例之意而已。初非以诚敬。分别于天人而为言也。朱子又尝论程子此说曰。天地也。似有个主宰。方是恁地变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无四边渗漏。便无走作。以此说观之。或若复问天道之于敬如何云尔。则未知朱子所答竟如何也。公曰。所论甚善矣。复进曰。敢问敬之为义。公曰。先儒备言之。于程子尹氏谢氏之说可见。曰。鄙生窃意三说。非敬之实也。曰。何以言之。曰。所谓整齐也。严肃也。惺惺也。收敛也。即所以敬之事。而非敬之实。如孔门教为仁。以四勿敬恕。四勿敬恕。即所以为仁。而非四勿敬恕。便是仁也。恐先儒论为敬之事。而人直作敬看。故闻天道。亦敬之说。则莫不为骇以为天何尝整齐严肃惺惺收敛。不知天道自然
意。而其言及于天道。初非因程子说而为之主张也。(程子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于其中。只是敬。公劄以为因是说而为言云云。)然今以劄中所引朱子说观之。(或问程子曰云云。如何。朱子曰。易是自然底造化。圣人只说造化流行。不敬便间断了。前辈引经文。多是借来说己意云云。公劄又引此说以明之。)盖程子因经中存存之语。推作学者敬之张本。非直解本文之义者。故朱子特说破其引经变例之意而已。初非以诚敬。分别于天人而为言也。朱子又尝论程子此说曰。天地也。似有个主宰。方是恁地变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无四边渗漏。便无走作。以此说观之。或若复问天道之于敬如何云尔。则未知朱子所答竟如何也。公曰。所论甚善矣。复进曰。敢问敬之为义。公曰。先儒备言之。于程子尹氏谢氏之说可见。曰。鄙生窃意三说。非敬之实也。曰。何以言之。曰。所谓整齐也。严肃也。惺惺也。收敛也。即所以敬之事。而非敬之实。如孔门教为仁。以四勿敬恕。四勿敬恕。即所以为仁。而非四勿敬恕。便是仁也。恐先儒论为敬之事。而人直作敬看。故闻天道。亦敬之说。则莫不为骇以为天何尝整齐严肃惺惺收敛。不知天道自然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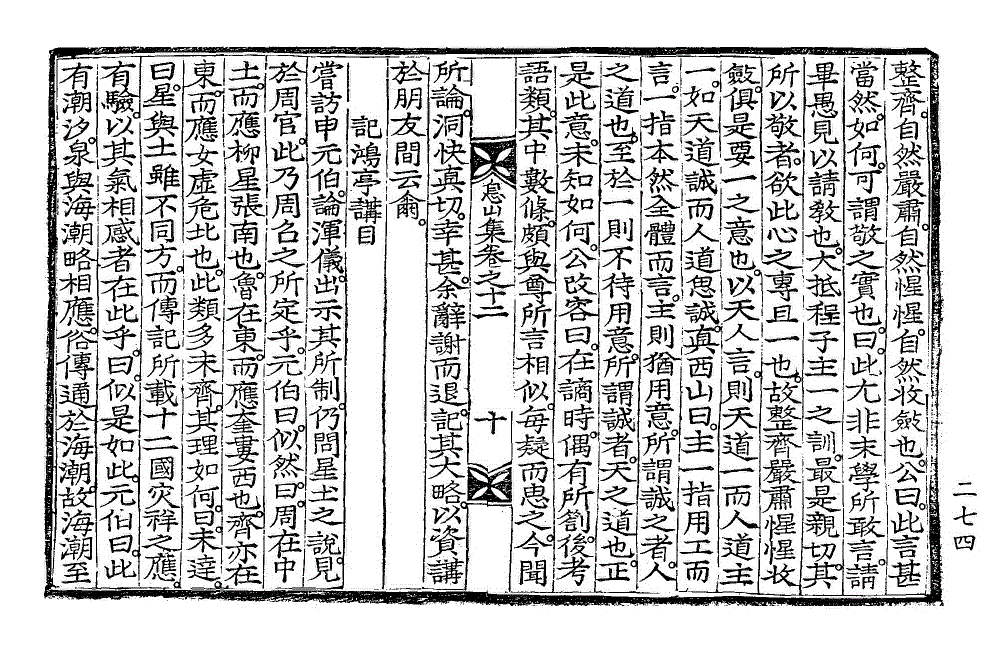 整齐。自然严肃。自然惺惺。自然收敛也。公曰。此言甚当然。如何。可谓敬之实也。曰。此尤非末学所敢言。请毕愚见以请教也。大抵程子主一之训。最是亲切。其所以敬者。欲此心之专且一也。故整齐严肃惺惺收敛。俱是要一之意也。以天人言。则天道一而人道主一。如天道诚而人道思诚。真西山曰。主一指用工而言。一指本然全体而言。主则犹用意。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至于一则不待用意。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正是此意。未知如何。公改容曰。在谪时。偶有所劄。后考语类。其中数条。颇与尊所言相似。每疑而思之。今闻所论。洞快真切。幸甚。余辞谢而退。记其大略。以资讲于朋友间云尔。
整齐。自然严肃。自然惺惺。自然收敛也。公曰。此言甚当然。如何。可谓敬之实也。曰。此尤非末学所敢言。请毕愚见以请教也。大抵程子主一之训。最是亲切。其所以敬者。欲此心之专且一也。故整齐严肃惺惺收敛。俱是要一之意也。以天人言。则天道一而人道主一。如天道诚而人道思诚。真西山曰。主一指用工而言。一指本然全体而言。主则犹用意。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至于一则不待用意。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正是此意。未知如何。公改容曰。在谪时。偶有所劄。后考语类。其中数条。颇与尊所言相似。每疑而思之。今闻所论。洞快真切。幸甚。余辞谢而退。记其大略。以资讲于朋友间云尔。记鸿亭讲目
尝访申元伯。论浑仪。出示其所制。仍问星土之说。见于周官。此乃周召之所定乎。元伯曰。似然。曰。周在中土。而应柳星张南也。鲁在东。而应奎娄西也。齐亦在东。而应女虚危北也。此类多未齐。其理如何。曰。未达。曰。星与土虽不同方。而传记所载十二国灾祥之应。有验。以其气相感者在此乎。曰。似是如此。元伯曰。此有潮汐。泉与海潮略相应。俗传通于海潮。故海潮至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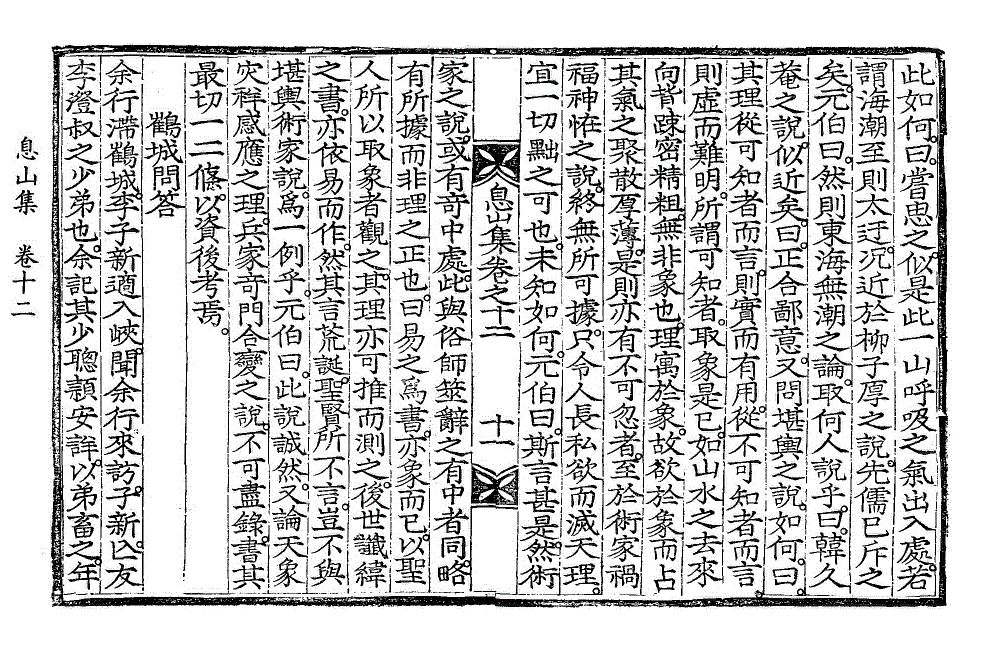 此如何。曰。尝思之。似是此一山呼吸之气出入处。若谓海潮至则太迂。况近于柳子厚之说。先儒已斥之矣。元伯曰。然则东海无潮之论。取何人说乎。曰。韩久庵之说。似近矣。曰。正合鄙意。又问堪舆之说。如何。曰。其理从可知者而言。则实而有用。从不可知者而言。则虚而难明。所谓可知者。取象是已。如山水之去来向背疏密精粗。无非象也。理寓于象。故欲于象而占其气之聚散厚薄。是则亦有不可忽者。至于术家祸福神怪之说。终无所可据。只令人长私欲而灭天理。宜一切黜之可也。未知如何。元伯曰。斯言甚是。然术家之说。或有奇中处。此与俗师筮辞之有中者同。略有所据而非理之正也。曰易之为书。亦象而已。以圣人所以取象者观之。其理亦可推而测之。后世谶纬之书。亦依易而作。然其言荒诞。圣贤所不言。岂不与堪舆术家说。为一例乎。元伯曰。此说诚然。又论天象灾祥感应之理。兵家奇门合变之说。不可尽录。书其最切一二条。以资后考焉。
此如何。曰。尝思之。似是此一山呼吸之气出入处。若谓海潮至则太迂。况近于柳子厚之说。先儒已斥之矣。元伯曰。然则东海无潮之论。取何人说乎。曰。韩久庵之说。似近矣。曰。正合鄙意。又问堪舆之说。如何。曰。其理从可知者而言。则实而有用。从不可知者而言。则虚而难明。所谓可知者。取象是已。如山水之去来向背疏密精粗。无非象也。理寓于象。故欲于象而占其气之聚散厚薄。是则亦有不可忽者。至于术家祸福神怪之说。终无所可据。只令人长私欲而灭天理。宜一切黜之可也。未知如何。元伯曰。斯言甚是。然术家之说。或有奇中处。此与俗师筮辞之有中者同。略有所据而非理之正也。曰易之为书。亦象而已。以圣人所以取象者观之。其理亦可推而测之。后世谶纬之书。亦依易而作。然其言荒诞。圣贤所不言。岂不与堪舆术家说。为一例乎。元伯曰。此说诚然。又论天象灾祥感应之理。兵家奇门合变之说。不可尽录。书其最切一二条。以资后考焉。鹤城问答
余行滞鹤城。李子新适入峡。闻余行来访。子新。亡友李澄叔之少弟也。余记其少聪颖安详。以弟畜之。年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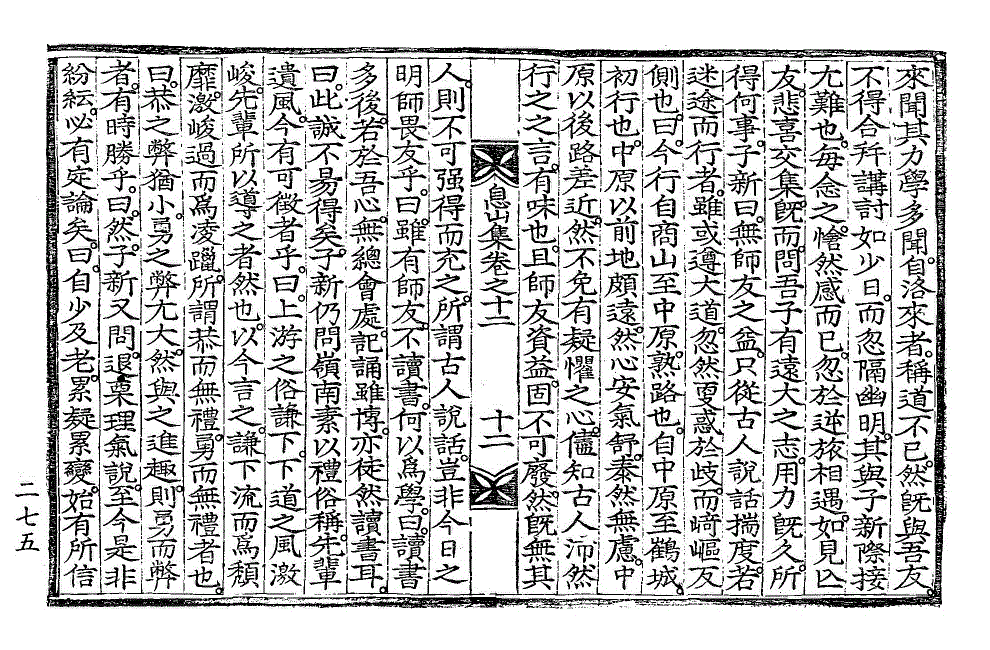 来闻其力学多闻。自洛来者。称道不已。然既与吾友。不得合并讲讨如少日。而忽隔幽明。其与子新际接尤难也。每念之。怆然感而已。忽于逆旅相遇。如见亡友。悲喜交集。既而。问吾子有远大之志。用力既久。所得何事。子新曰。无师友之益。只从古人说话揣度。若迷途而行者。虽或遵大道。忽然更惑于歧。而崎岖反侧也。曰。今行自商山至中原。熟路也。自中原至鹤城。初行也。中原以前地颇远。然心安气舒。泰然无虑。中原以后路差近。然不免有疑惧之心。尽知古人沛然行之之言。有味也。且师友资益。固不可废。然既无其人。则不可强得而充之。所谓古人说话。岂非今日之明师畏友乎。曰。虽有师友。不读书。何以为学。曰。读书多后。若于吾心。无总会处。记诵虽博。亦徒然读书耳。曰。此诚不易得矣。子新仍问岭南素以礼俗称。先辈遗风。今有可徵者乎。曰。上游之俗谦下。下道之风激峻。先辈所以导之者然也。以今言之。谦下流而为颓靡。激峻过而为凌躐。所谓恭而无礼。勇而无礼者也。曰。恭之弊犹小。勇之弊尤大。然与之进趣。则勇而弊者。有时胜乎。曰。然。子新又问。退,栗理气说。至今是非纷纭。必有定论矣。曰。自少及老。累疑累变。始有所信
来闻其力学多闻。自洛来者。称道不已。然既与吾友。不得合并讲讨如少日。而忽隔幽明。其与子新际接尤难也。每念之。怆然感而已。忽于逆旅相遇。如见亡友。悲喜交集。既而。问吾子有远大之志。用力既久。所得何事。子新曰。无师友之益。只从古人说话揣度。若迷途而行者。虽或遵大道。忽然更惑于歧。而崎岖反侧也。曰。今行自商山至中原。熟路也。自中原至鹤城。初行也。中原以前地颇远。然心安气舒。泰然无虑。中原以后路差近。然不免有疑惧之心。尽知古人沛然行之之言。有味也。且师友资益。固不可废。然既无其人。则不可强得而充之。所谓古人说话。岂非今日之明师畏友乎。曰。虽有师友。不读书。何以为学。曰。读书多后。若于吾心。无总会处。记诵虽博。亦徒然读书耳。曰。此诚不易得矣。子新仍问岭南素以礼俗称。先辈遗风。今有可徵者乎。曰。上游之俗谦下。下道之风激峻。先辈所以导之者然也。以今言之。谦下流而为颓靡。激峻过而为凌躐。所谓恭而无礼。勇而无礼者也。曰。恭之弊犹小。勇之弊尤大。然与之进趣。则勇而弊者。有时胜乎。曰。然。子新又问。退,栗理气说。至今是非纷纭。必有定论矣。曰。自少及老。累疑累变。始有所信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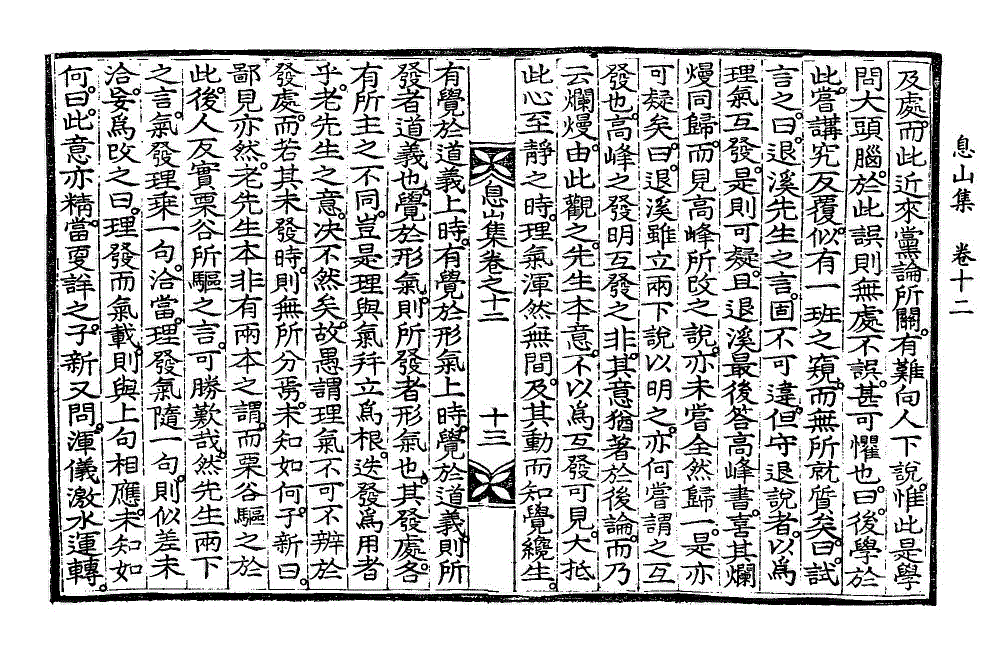 及处。而此近来党论所关。有难向人下说。惟此是学问大头脑。于此误则无处不误。甚可惧也。曰。后学于此。尝讲究反覆。似有一班之窥。而无所就质矣。曰。试言之。曰。退溪先生之言。固不可违。但守退说者。以为理气互发。是则可疑。且退溪最后答高峰书。喜其烂熳同归。而见高峰所改之说。亦未尝全然归一。是亦可疑矣。曰。退溪虽立两下说以明之。亦何尝谓之互发也。高峰之发明互发之非。其意犹著于后论。而乃云烂熳。由此观之。先生本意。不以为互发可见。大抵此心至静之时。理气浑然无间。及其动而知觉才生。有觉于道义上时。有觉于形气上时。觉于道义。则所发者道义也。觉于形气。则所发者形气也。其发处。各有所主之不同。岂是理与气并立为根。迭发为用者乎。老先生之意。决不然矣。故愚谓理气不可不辨于发处。而若其未发时。则无所分焉。未知如何。子新曰。鄙见亦然。老先生本非有两本之谓。而栗谷驱之于此。后人反实栗谷所驱之言。可胜叹哉。然先生两下之言。气发理乘一句。洽当。理发气随一句。则似差未洽。妄为改之曰。理发而气载。则与上句相应。未知如何。曰。此意亦精。当更详之。子新又问。浑仪激水运转。
及处。而此近来党论所关。有难向人下说。惟此是学问大头脑。于此误则无处不误。甚可惧也。曰。后学于此。尝讲究反覆。似有一班之窥。而无所就质矣。曰。试言之。曰。退溪先生之言。固不可违。但守退说者。以为理气互发。是则可疑。且退溪最后答高峰书。喜其烂熳同归。而见高峰所改之说。亦未尝全然归一。是亦可疑矣。曰。退溪虽立两下说以明之。亦何尝谓之互发也。高峰之发明互发之非。其意犹著于后论。而乃云烂熳。由此观之。先生本意。不以为互发可见。大抵此心至静之时。理气浑然无间。及其动而知觉才生。有觉于道义上时。有觉于形气上时。觉于道义。则所发者道义也。觉于形气。则所发者形气也。其发处。各有所主之不同。岂是理与气并立为根。迭发为用者乎。老先生之意。决不然矣。故愚谓理气不可不辨于发处。而若其未发时。则无所分焉。未知如何。子新曰。鄙见亦然。老先生本非有两本之谓。而栗谷驱之于此。后人反实栗谷所驱之言。可胜叹哉。然先生两下之言。气发理乘一句。洽当。理发气随一句。则似差未洽。妄为改之曰。理发而气载。则与上句相应。未知如何。曰。此意亦精。当更详之。子新又问。浑仪激水运转。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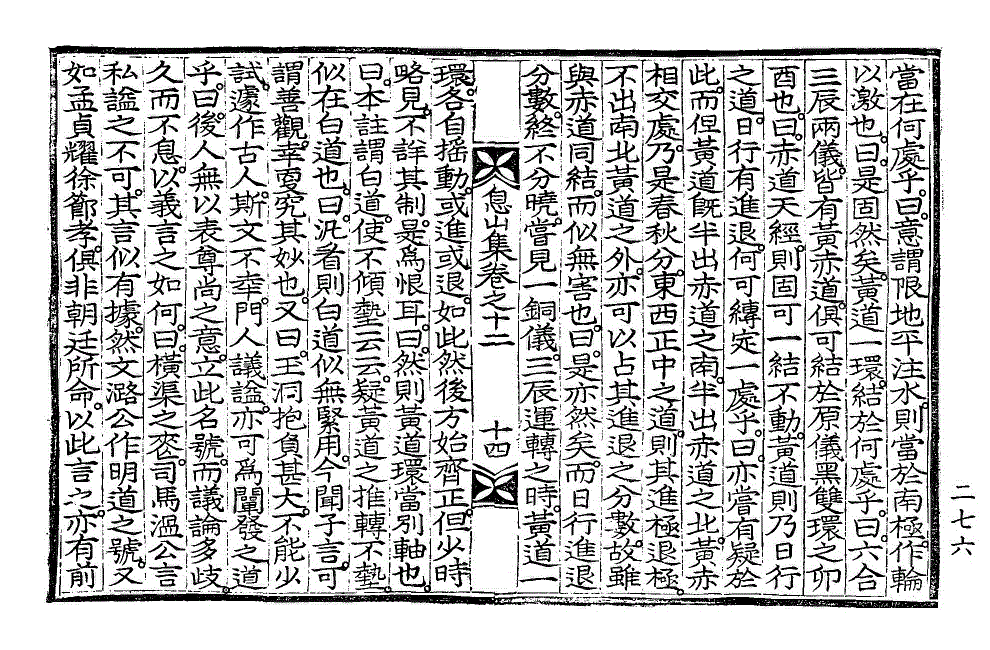 当在何处乎。曰。意谓限地平注水。则当于南极。作轮以激也。曰。是固然矣。黄道一环。结于何处乎。曰。六合三辰两仪。皆有黄赤道。俱可结于原仪黑双环之卯酉也。曰。赤道天经。则固可一结不动。黄道则乃日行之道。日行有进退。何可縳定一处乎。曰。亦尝有疑于此。而但黄道既半出赤道之南。半出赤道之北。黄赤相交处。乃是春秋分。东西正中之道。则其进极退极。不出南北黄道之外。亦可以占其进退之分数。故虽与赤道同结。而似无害也。曰。是亦然矣。而日行进退分数。终不分晓。尝见一铜仪。三辰运转之时。黄道一环。各自摇动。或进或退。如此然后方始齐正。但少时略见。不详其制。是为恨耳。曰。然则黄道环当别轴也。曰。本注谓白道。使不倾垫云云。疑黄道之推转不垫。似在白道也。曰。汎看则白道似无紧用。今闻子言。可谓善观。幸更究其妙也。又曰。玉洞抱负甚大。不能少试。遽作古人。斯文不幸。门人议谥。亦可为阐发之道乎。曰。后人无以表尊尚之意。立此名号。而议论多歧。久而不息。以义言之如何。曰。横渠之丧。司马温公言私谥之不可。其言似有据。然文潞公作明道之号。又如孟贞耀徐节孝。俱非朝廷所命。以此言之。亦有前
当在何处乎。曰。意谓限地平注水。则当于南极。作轮以激也。曰。是固然矣。黄道一环。结于何处乎。曰。六合三辰两仪。皆有黄赤道。俱可结于原仪黑双环之卯酉也。曰。赤道天经。则固可一结不动。黄道则乃日行之道。日行有进退。何可縳定一处乎。曰。亦尝有疑于此。而但黄道既半出赤道之南。半出赤道之北。黄赤相交处。乃是春秋分。东西正中之道。则其进极退极。不出南北黄道之外。亦可以占其进退之分数。故虽与赤道同结。而似无害也。曰。是亦然矣。而日行进退分数。终不分晓。尝见一铜仪。三辰运转之时。黄道一环。各自摇动。或进或退。如此然后方始齐正。但少时略见。不详其制。是为恨耳。曰。然则黄道环当别轴也。曰。本注谓白道。使不倾垫云云。疑黄道之推转不垫。似在白道也。曰。汎看则白道似无紧用。今闻子言。可谓善观。幸更究其妙也。又曰。玉洞抱负甚大。不能少试。遽作古人。斯文不幸。门人议谥。亦可为阐发之道乎。曰。后人无以表尊尚之意。立此名号。而议论多歧。久而不息。以义言之如何。曰。横渠之丧。司马温公言私谥之不可。其言似有据。然文潞公作明道之号。又如孟贞耀徐节孝。俱非朝廷所命。以此言之。亦有前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7H 页
 證矣。曰。自古私谥。非但孟,徐而已。我朝亦有之云矣。惟我两兄平日与吾丈。许以道义。其一生行谊心事。吾丈必知吾辈所不及知者多矣。显刻文字。幸有以留意也。曰。子之有此言。宜矣。余虽无文。何敢辞诸。如得赖天之灵。得个意思而卒业焉。庶不负仲叔于泉下耳。
證矣。曰。自古私谥。非但孟,徐而已。我朝亦有之云矣。惟我两兄平日与吾丈。许以道义。其一生行谊心事。吾丈必知吾辈所不及知者多矣。显刻文字。幸有以留意也。曰。子之有此言。宜矣。余虽无文。何敢辞诸。如得赖天之灵。得个意思而卒业焉。庶不负仲叔于泉下耳。华阴日录抄
积雪初晴。拓蓬户。看峡山。岩峦装以银玉插天。爽然开睡眸。清盥危坐。体验气象。若如彼一般。
命奴凿壁。造曲窟。将以燃松看书。或问何以为此。曰。坐无油也。曰。此虽照室。眼致涩泪。衣易染缁。益少害多矣。曰。凡世人所谓益者。又孰无害于其中乎。松者。取之不难。用之甚切。如使窟也。高其脑凹其口。亦不至于涩泪。若衣之缁则无伤也。孰知白之不缁缁之复白耶。
全休甫来访。请闻山居乐事。曰。土突甚温。隆寒可以薄絮御之。夜爇松明。玩绎书史。朝起盥濯。凝神块坐。心地虚净。无一物来相引诱。时开户看山。远近列岫。俱若迎拜。吟啸傲睨。时起缓步。亦有閒暇自得之趣。此即目前事也。若其四时佳兴。必有随时而新者矣。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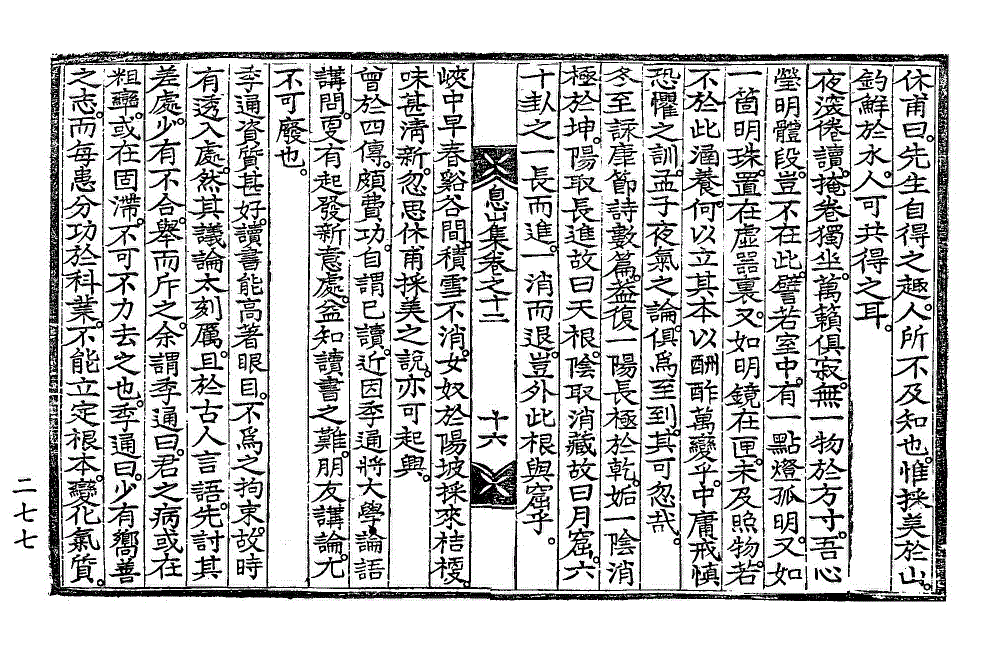 休甫曰。先生自得之趣。人所不及知也。惟采美于山。钓鲜于水。人可共得之耳。
休甫曰。先生自得之趣。人所不及知也。惟采美于山。钓鲜于水。人可共得之耳。夜深倦读。掩卷独坐。万籁俱寂。无一物于方寸。吾心莹明体段。岂不在此。譬若室中。有一点灯孤明。又如一个明珠。置在虚器里。又如明镜在匣。未及照物。若不于此涵养。何以立其本以酬酢万变乎。中庸戒慎恐惧之训。孟子夜气之论。俱为至到。其可忽哉。
冬至咏康节诗数篇。盖复一阳长极于乾。姤一阴消极于坤。阳取长进故曰天根。阴取消藏故曰月窟。六十卦之一长而进。一消而退。岂外此根与窟乎。
峡中早春溪谷间。积雪不消。女奴于阳坡采来桔梗。味甚清新。忽思休甫采美之说。亦可起兴。
曾于四传。颇费功。自谓已读。近因季通将大学,论语讲问。更有起发新意处。益知读书之难。朋友讲论。尤不可废也。
季通资质甚好。读书能高著眼目。不为之拘束。故时有透入处。然其议论太刻厉。且于古人言语。先讨其差处。少有不合。举而斥之。余谓季通曰。君之病或在粗率。或在固滞。不可不力去之也。季通曰。少有向善之志。而每患分功于科业。不能立定根本。变化气质。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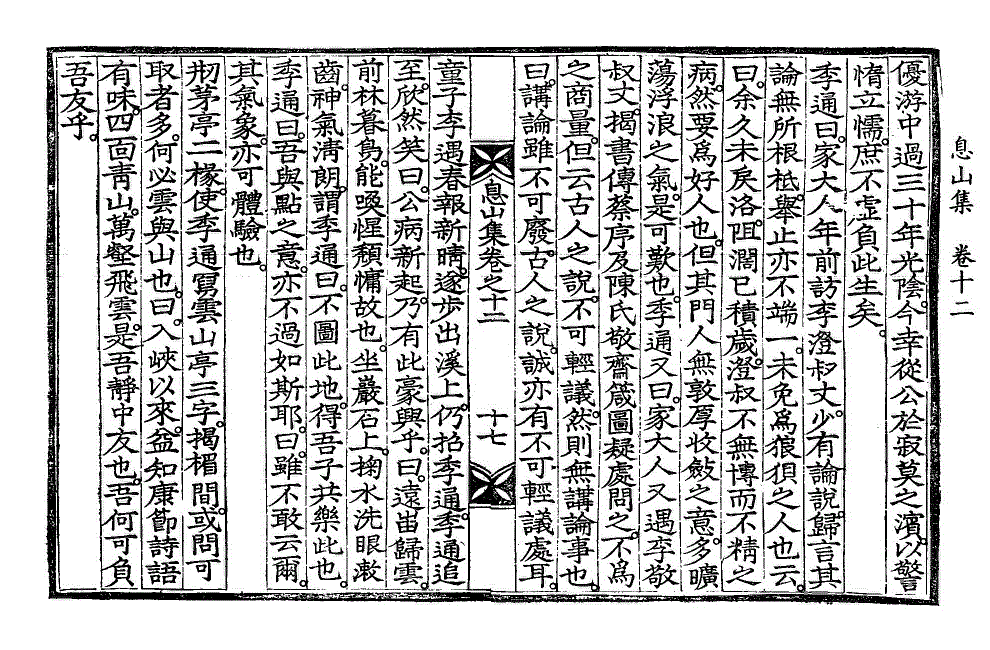 优游中过三十年光阴。今幸从公于寂莫之滨。以警惰立懦。庶不虚负此生矣。
优游中过三十年光阴。今幸从公于寂莫之滨。以警惰立懦。庶不虚负此生矣。季通曰。家大人年前访李澄叔丈。少有论说。归言其论无所根柢。举止亦不端一。未免为狼狈之人也云。曰。余久未戾洛。阻阔已积岁。澄叔不无博而不精之病。然要为好人也。但其门人无敦厚收敛之意。多旷荡浮浪之气。是可叹也。季通又曰。家大人又遇李敬叔丈。揭书传蔡序及陈氏敬斋箴图疑处问之。不为之商量。但云古人之说。不可轻议。然则无讲论事也。曰。讲论虽不可废。古人之说。诚亦有不可轻议处耳。童子李遇春报新晴。遂步出溪上。仍招季通。季通追至。欣然笑曰。公病新起。乃有此豪兴乎。曰。远岫归云。前林暮鸟。能唤惺颓慵故也。坐岩石上。掬水洗眼漱齿。神气清朗。谓季通曰。不图此地。得吾子共乐此也。季通曰。吾与点之意。亦不过如斯耶。曰。虽不敢云尔。其气象。亦可体验也。
刱茅亭二椽。使季通写云山亭三字。揭楣间。或问可取者多。何必云与山也。曰。入峡以来。益知康节诗语有味。四面青山。万壑飞云。是吾静中友也。吾何可负吾友乎。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8L 页
 学钓于老苍头。早出溪上。易岩而坐。不觉入谷转深。苍头断蚯蚓为饵。余不忍。包饭而代。鱼之求饵者。舍饭而取蚓。余终日而不得一鱼。苍头曰。此非法故也。余曰。吾取适。非取鱼也。苍头能善吹箫。向晚使吹一声。倚岩垂纶而听之。亦一佳趣也。第三日。苍头请易钓竿。遂将蚓饵投之。果有一大鱼含出。令人失笑。将此事归语季通。季通曰。违法不成。事莫不然。此可以喻大矣。曰。人之求利也。舍饭取蚓者滔滔。不亦异乎。近读离骚诸篇。童子李遇春问曰。先生读圣贤书。咿唔而已。今读离骚。声若金石。或慷慨呜咽。其有所感乎。曰。童子知之。凡读离骚。不激感者。非忠臣与志士也。
学钓于老苍头。早出溪上。易岩而坐。不觉入谷转深。苍头断蚯蚓为饵。余不忍。包饭而代。鱼之求饵者。舍饭而取蚓。余终日而不得一鱼。苍头曰。此非法故也。余曰。吾取适。非取鱼也。苍头能善吹箫。向晚使吹一声。倚岩垂纶而听之。亦一佳趣也。第三日。苍头请易钓竿。遂将蚓饵投之。果有一大鱼含出。令人失笑。将此事归语季通。季通曰。违法不成。事莫不然。此可以喻大矣。曰。人之求利也。舍饭取蚓者滔滔。不亦异乎。近读离骚诸篇。童子李遇春问曰。先生读圣贤书。咿唔而已。今读离骚。声若金石。或慷慨呜咽。其有所感乎。曰。童子知之。凡读离骚。不激感者。非忠臣与志士也。客自洞口而来。至则乃李孟源也。余迎于云山亭。执手曰。空谷跫音亦喜。况君乎。孟源曰。适自江左归松面。迂路来访。为叙积阻怀也。时朝雨乍收。烟岚羃岫。孟源弊衣弊冠半湿。气宇轩昂。论议慷慨。真是风流出尘之士也。余曰。与君久不相见。今幸得从容。岂非天与也。君既谢绝名利。何不一意从事于大中至正之学。以君颖隽卓秀。复路而来。他人勤苦未得。一超可至。岂不尤洒落奇伟乎。孟源曰。我自少好古文。颇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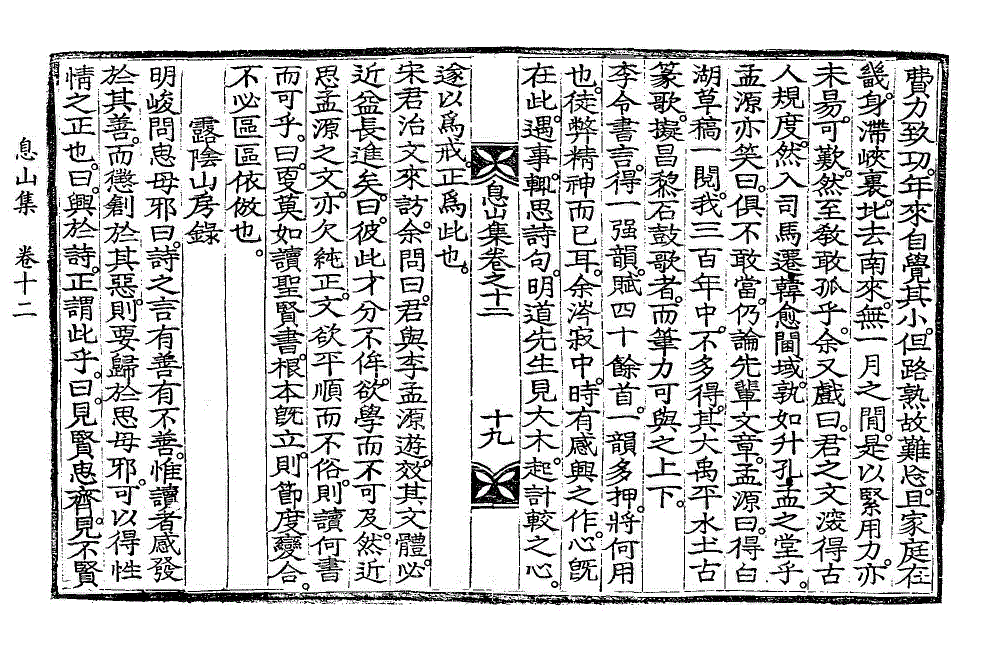 费力致功。年来自觉其小。但路熟故难忘。且家庭在畿。身滞峡里。北去南来。无一月之閒。是以紧用力。亦未易。可叹。然至教敢孤乎。余又戏曰。君之文深得古人规度。然入司马迁,韩愈阃域。孰如升孔,孟之堂乎。孟源亦笑曰。俱不敢当。仍论先辈文章。孟源曰。得白湖草稿一阅。我三百年中。不多得。其大禹平水土古篆歌。拟昌黎石鼓歌者。而笔力可与之上下。
费力致功。年来自觉其小。但路熟故难忘。且家庭在畿。身滞峡里。北去南来。无一月之閒。是以紧用力。亦未易。可叹。然至教敢孤乎。余又戏曰。君之文深得古人规度。然入司马迁,韩愈阃域。孰如升孔,孟之堂乎。孟源亦笑曰。俱不敢当。仍论先辈文章。孟源曰。得白湖草稿一阅。我三百年中。不多得。其大禹平水土古篆歌。拟昌黎石鼓歌者。而笔力可与之上下。李令书言。得一强韵。赋四十馀首。一韵多押。将何用也。徒弊精神而已耳。余涔寂中。时有感兴之作。心既在此。遇事。辄思诗句。明道先生见大木。起计较之心。遂以为戒。正为此也。
宋君治文来访。余问曰。君与李孟源游。效其文体。必近益长进矣。曰。彼此才分不侔。欲学而不可及。然近思孟源之文。亦欠纯正。文欲平顺而不俗。则读何书而可乎。曰。更莫如读圣贤书。根本既立。则节度变合。不必区区依仿也。
露阴山房录
明峻问思毋邪曰。诗之言有善有不善。惟读者感发于其善。而惩创于其恶。则要归于思毋邪。可以得性情之正也。曰。兴于诗。正谓此乎。曰。见贤思齐。见不贤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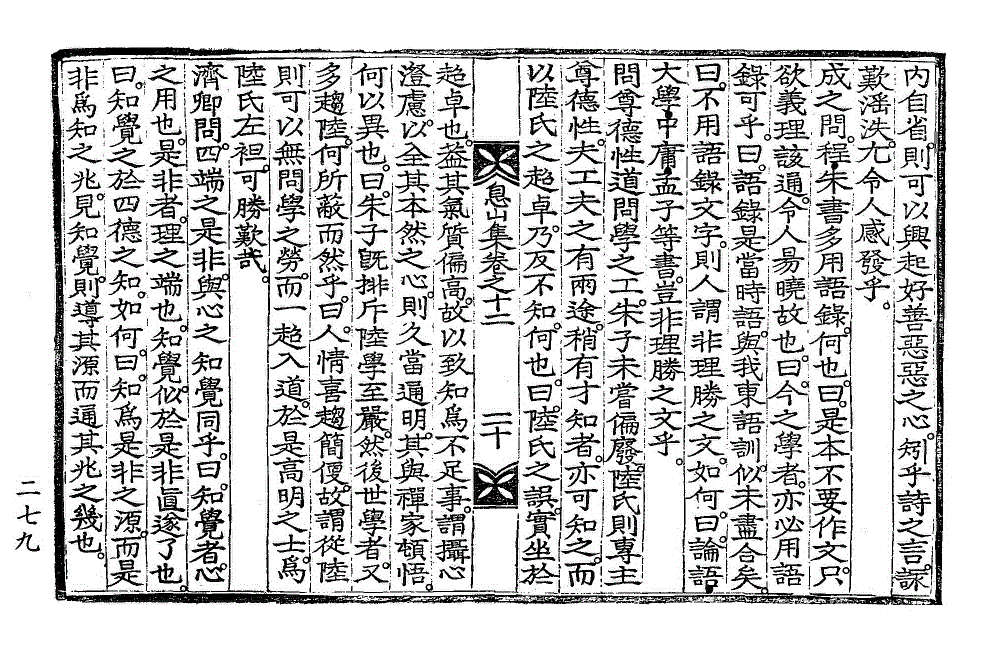 内自省。则可以兴起好善恶恶之心。矧乎诗之言。咏叹淫泆。尤令人感发乎。
内自省。则可以兴起好善恶恶之心。矧乎诗之言。咏叹淫泆。尤令人感发乎。成之问。程,朱书多用语录。何也。曰。是本不要作文。只欲义理该通。令人易晓故也。曰。今之学者。亦必用语录可乎。曰。语录是当时语。与我东语训。似未尽合矣。曰。不用语录文字。则人谓非理胜之文。如何。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岂非理胜之文乎。
问尊德性道问学之工。朱子未尝偏废。陆氏则专主尊德性。夫工夫之有两途。稍有才知者。亦可知之。而以陆氏之超卓。乃反不知。何也。曰。陆氏之误。实坐于超卓也。盖其气质偏高。故以致知为不足事。谓摄心澄虑。以全其本然之心。则久当通明。其与禅家顿悟。何以异也。曰。朱子既排斥陆学至严。然后世学者。又多趋陆。何所蔽而然乎。曰。人情喜趋简便。故谓从陆则可以无问学之劳。而一超入道。于是高明之士。为陆氏左袒。可胜叹哉。
济卿问。四端之是非。与心之知觉同乎。曰。知觉者。心之用也。是非者。理之端也。知觉。似于是非直遂了也。曰。知觉之于四德之知。如何。曰。知为是非之源。而是非为知之兆。见知觉。则导其源而通其兆之几也。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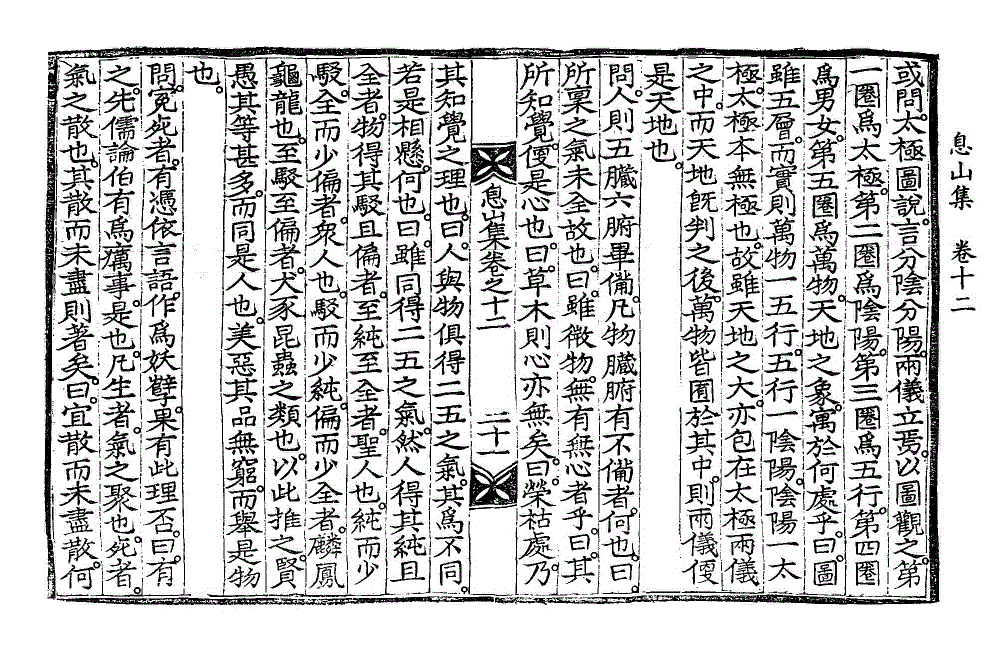 或问。太极图说。言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以图观之。第一圈为太极。第二圈为阴阳。第三圈为五行。第四圈为男女。第五圈为万物。天地之象。寓于何处乎。曰。图虽五层。而实则万物一五行。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故虽天地之大。亦包在太极两仪之中。而天地既判之后。万物皆囿于其中。则两仪便是天地也。
或问。太极图说。言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以图观之。第一圈为太极。第二圈为阴阳。第三圈为五行。第四圈为男女。第五圈为万物。天地之象。寓于何处乎。曰。图虽五层。而实则万物一五行。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故虽天地之大。亦包在太极两仪之中。而天地既判之后。万物皆囿于其中。则两仪便是天地也。问。人则五脏六腑毕备。凡物脏腑有不备者。何也。曰。所禀之气未全故也。曰。虽微物。无有无心者乎。曰。其所知觉。便是心也。曰。草木则心亦无矣。曰。荣枯处。乃其知觉之理也。曰。人与物俱得二五之气。其为不同。若是相悬。何也。曰。虽同得二五之气。然人得其纯且全者。物得其驳且偏者。至纯至全者。圣人也。纯而少驳。全而少偏者。众人也。驳而少纯。偏而少全者。麟凤龟龙也。至驳至偏者。犬豕昆虫之类也。以此推之。贤愚其等甚多。而同是人也。美恶其品无穷。而举是物也。
问。冤死者。有凭依言语。作为妖孽。果有此理否。曰。有之。先儒论伯有为疠事。是也。凡生者。气之聚也。死者。气之散也。其散而未尽则著矣。曰。宜散而未尽散。何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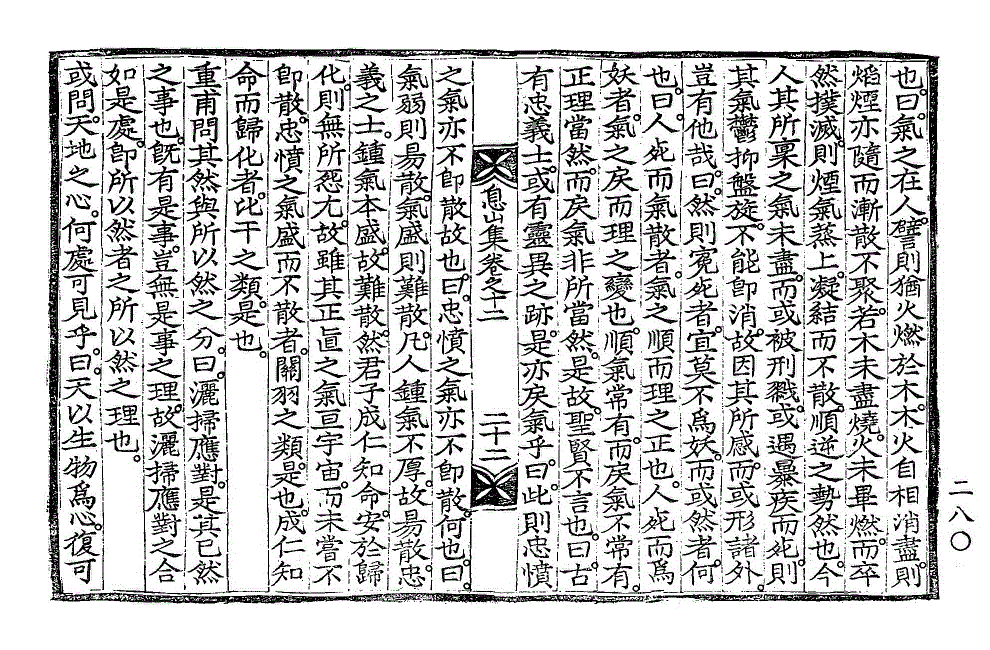 也。曰。气之在人。譬则犹火燃于木。木火自相消尽。则焰烟亦随而渐散不聚。若木未尽烧。火未毕燃。而卒然扑灭。则烟气蒸上。凝结而不散。顺逆之势然也。今人其所禀之气未尽。而或被刑戮。或遇㬥疾而死。则其气郁抑盘旋。不能即消。故因其所感。而或形诸外。岂有他哉。曰。然则冤死者。宜莫不为妖。而或然者。何也。曰。人死而气散者。气之顺而理之正也。人死而为妖者。气之戾而理之变也。顺气常有。而戾气不常有。正理当然。而戾气非所当然。是故。圣贤不言也。曰。古有忠义士。或有灵异之迹。是亦戾气乎。曰。此则忠愤之气亦不即散故也。曰。忠愤之气亦不即散。何也。曰。气弱则易散。气盛则难散。凡人钟气不厚。故易散。忠义之士。钟气本盛。故难散。然君子成仁知命。安于归化。则无所怨尤。故虽其正直之气亘宇宙。而未尝不即散。忠愤之气盛而不散者。关羽之类。是也。成仁知命而归化者。比干之类。是也。
也。曰。气之在人。譬则犹火燃于木。木火自相消尽。则焰烟亦随而渐散不聚。若木未尽烧。火未毕燃。而卒然扑灭。则烟气蒸上。凝结而不散。顺逆之势然也。今人其所禀之气未尽。而或被刑戮。或遇㬥疾而死。则其气郁抑盘旋。不能即消。故因其所感。而或形诸外。岂有他哉。曰。然则冤死者。宜莫不为妖。而或然者。何也。曰。人死而气散者。气之顺而理之正也。人死而为妖者。气之戾而理之变也。顺气常有。而戾气不常有。正理当然。而戾气非所当然。是故。圣贤不言也。曰。古有忠义士。或有灵异之迹。是亦戾气乎。曰。此则忠愤之气亦不即散故也。曰。忠愤之气亦不即散。何也。曰。气弱则易散。气盛则难散。凡人钟气不厚。故易散。忠义之士。钟气本盛。故难散。然君子成仁知命。安于归化。则无所怨尤。故虽其正直之气亘宇宙。而未尝不即散。忠愤之气盛而不散者。关羽之类。是也。成仁知命而归化者。比干之类。是也。重甫问其然与所以然之分。曰。洒扫应对。是其已然之事也。既有是事。岂无是事之理。故洒扫应对之合如是处。即所以然者之所以然之理也。
或问。天地之心。何处可见乎。曰。天以生物为心。复可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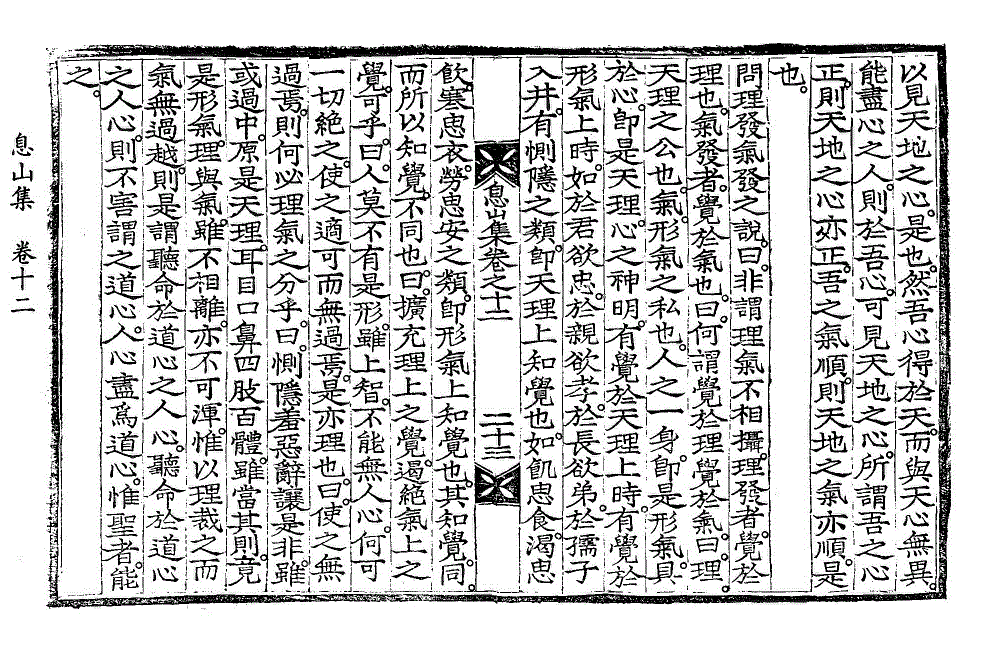 以见天地之心。是也。然吾心得于天。而与天心无异。能尽心之人。则于吾心。可见天地之心。所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也。
以见天地之心。是也。然吾心得于天。而与天心无异。能尽心之人。则于吾心。可见天地之心。所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也。问理发气发之说。曰。非谓理气不相摄。理发者。觉于理也。气发者。觉于气也。曰。何谓觉于理觉于气。曰。理。天理之公也。气。形气之私也。人之一身。即是形气。具于心。即是天理。心之神明。有觉于天理上时。有觉于形气上时。如于君欲忠。于亲欲孝。于长欲弟。于孺子入井。有恻隐之类。即天理上知觉也。如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劳思安之类。即形气上知觉也。其知觉。同。而所以知觉。不同也。曰。扩充理上之觉。遏绝气上之觉。可乎。曰。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何可一切绝之。使之适可而无过焉。是亦理也。曰。使之无过焉。则何必理气之分乎。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虽或过中。原是天理。耳目口鼻四肢百体。虽当其则。竟是形气。理与气。虽不相离。亦不可浑。惟以理裁之而气无过越。则是谓听命于道心之人心。听命于道心之人心。则不害谓之道心。人心尽为道心。惟圣者。能之。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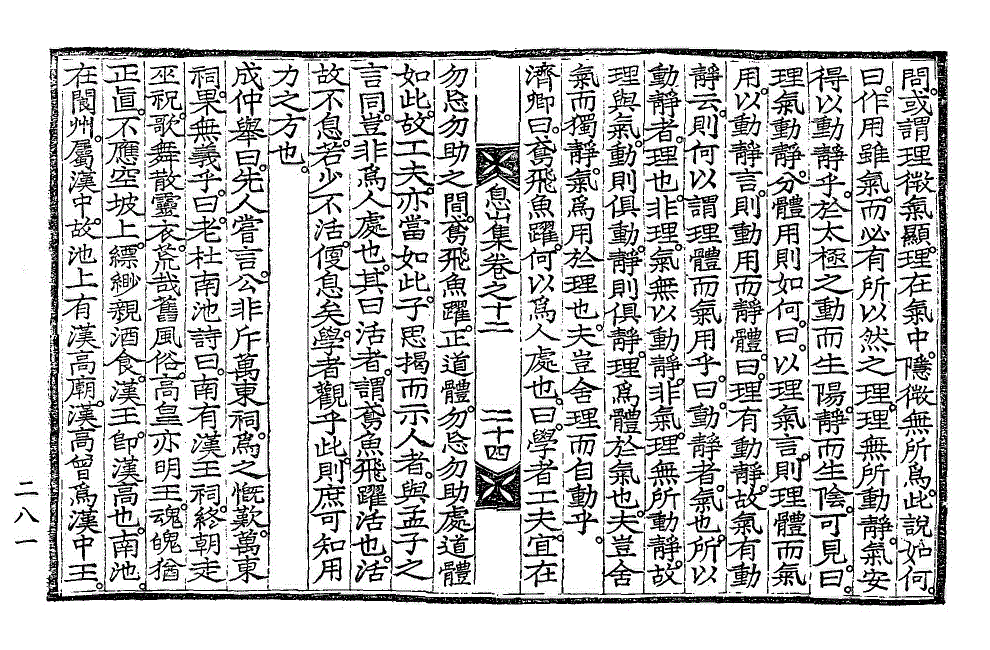 问。或谓理微气显。理在气中。隐微无所为。此说如何。曰。作用虽气。而必有所以然之理。理无所动静。气安得以动静乎。于太极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可见。曰。理气动静。分体用则如何。曰。以理气言。则理体而气用。以动静言。则动用而静体。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云。则何以谓理体而气用乎。曰。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非理。气无以动静。非气。理无所动静。故理与气。动则俱动。静则俱静。理为体于气也。夫岂舍气而独静。气为用于理也。夫岂舍理而自动乎。
问。或谓理微气显。理在气中。隐微无所为。此说如何。曰。作用虽气。而必有所以然之理。理无所动静。气安得以动静乎。于太极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可见。曰。理气动静。分体用则如何。曰。以理气言。则理体而气用。以动静言。则动用而静体。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云。则何以谓理体而气用乎。曰。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非理。气无以动静。非气。理无所动静。故理与气。动则俱动。静则俱静。理为体于气也。夫岂舍气而独静。气为用于理也。夫岂舍理而自动乎。济卿曰。鸢飞鱼跃。何以为人处也。曰。学者工夫。宜在勿忘勿助之间。鸢飞鱼跃。正道体。勿忘勿助处道体如此。故工夫。亦当如此。子思揭而示人者。与孟子之言同。岂非为人处也。其曰活者。谓鸢鱼飞跃活也。活故不息。若少不活。便息矣。学者观乎此。则庶可知用力之方也。
成仲举曰。先人尝言。公非斥万东祠。为之慨叹。万东祠。果无义乎。曰。老杜南池诗曰。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高皇亦明王。魂魄犹正直。不应空坡上。缥缈亲酒食。汉王。即汉高也。南池。在阆州。属汉中。故池上有汉高庙。汉高曾为汉中王。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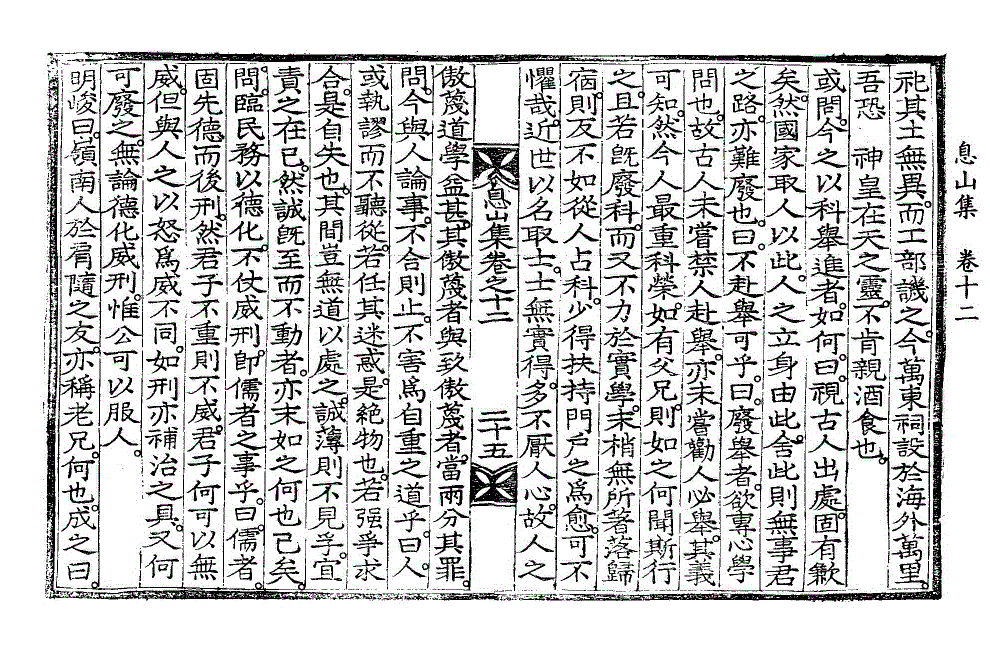 祀其土无异。而工部讥之。今万东祠设于海外万里。吾恐 神皇在天之灵。不肯亲酒食也。
祀其土无异。而工部讥之。今万东祠设于海外万里。吾恐 神皇在天之灵。不肯亲酒食也。或问。今之以科举进者。如何。曰。视古人出处。固有歉矣。然国家取人以此。人之立身由此。舍此则无事君之路。亦难废也。曰。不赴举可乎。曰。废举者。欲专心学问也。故古人未尝禁人赴举。亦未尝劝人必举。其义可知。然今人最重科荣。如有父兄。则如之何闻斯行之。且若既废科。而又不力于实学。末梢无所著落归宿。则反不如从人占科。少得扶持门户之为愈。可不惧哉。近世以名取士。士无实得。多不厌人心。故人之傲蔑道学益甚。其傲蔑者与致傲蔑者。当两分其罪。
问。今与人论事。不合则止。不害为自重之道乎。曰。人或执谬而不听从。若任其迷惑。是绝物也。若强争求合。是自失也。其间岂无道以处之。诚薄则不见孚。宜责之在己。然诚既至而不动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问。临民务以德化。不仗威刑。即儒者之事乎。曰。儒者。固先德而后刑。然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何可以无威。但与人之以怒为威不同。如刑亦补治之具。又何可废之。无论德化威刑。惟公可以服人。
明峻曰。岭南人于肩随之友。亦称老兄。何也。成之曰。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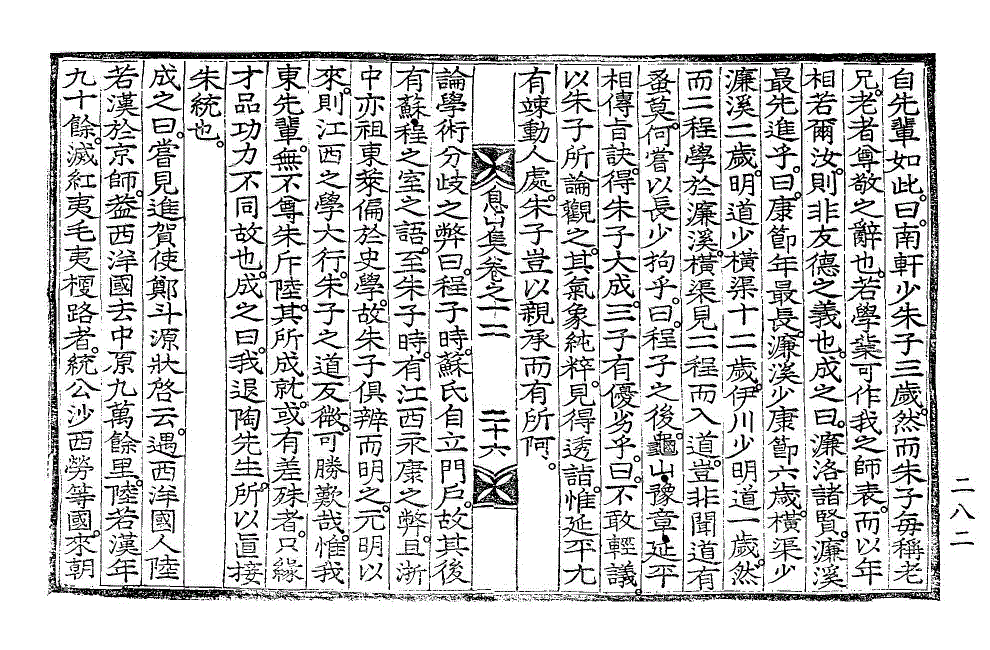 自先辈如此。曰。南轩少朱子三岁。然而朱子每称老兄。老者尊敬之辞也。若学业可作我之师表。而以年相若尔汝。则非友德之义也。成之曰。濂洛诸贤。濂溪最先进乎。曰。康节年最长。濂溪少康节六岁。横渠少濂溪二岁。明道少横渠十二岁。伊川少明道一岁。然而二程学于濂溪。横渠见二程而入道。岂非闻道有蚤莫。何尝以长少拘乎。曰。程子之后。龟山,豫章,延平相传旨诀。得朱子大成。三子有优劣乎。曰。不敢轻议。以朱子所论观之。其气象纯粹。见得透诣。惟延平尤有竦动人处。朱子岂以亲承而有所阿。
自先辈如此。曰。南轩少朱子三岁。然而朱子每称老兄。老者尊敬之辞也。若学业可作我之师表。而以年相若尔汝。则非友德之义也。成之曰。濂洛诸贤。濂溪最先进乎。曰。康节年最长。濂溪少康节六岁。横渠少濂溪二岁。明道少横渠十二岁。伊川少明道一岁。然而二程学于濂溪。横渠见二程而入道。岂非闻道有蚤莫。何尝以长少拘乎。曰。程子之后。龟山,豫章,延平相传旨诀。得朱子大成。三子有优劣乎。曰。不敢轻议。以朱子所论观之。其气象纯粹。见得透诣。惟延平尤有竦动人处。朱子岂以亲承而有所阿。论学术分歧之弊曰。程子时。苏氏自立门户。故其后有苏,程之室之语。至朱子时。有江西永康之弊。且浙中亦祖东莱偏于史学。故朱子俱辨而明之。元明以来。则江西之学大行。朱子之道反微。可胜叹哉。惟我东先辈。无不尊朱斥陆。其所成就。或有差殊者。只缘才品功力不同故也。成之曰。我退陶先生。所以直接朱统也。
成之曰。尝见进贺使郑斗源状启云。遇西洋国人陆若汉于京师。盖西洋国去中原九万馀里。陆若汉年九十馀。灭红夷毛夷梗路者。统公沙西劳等国。来朝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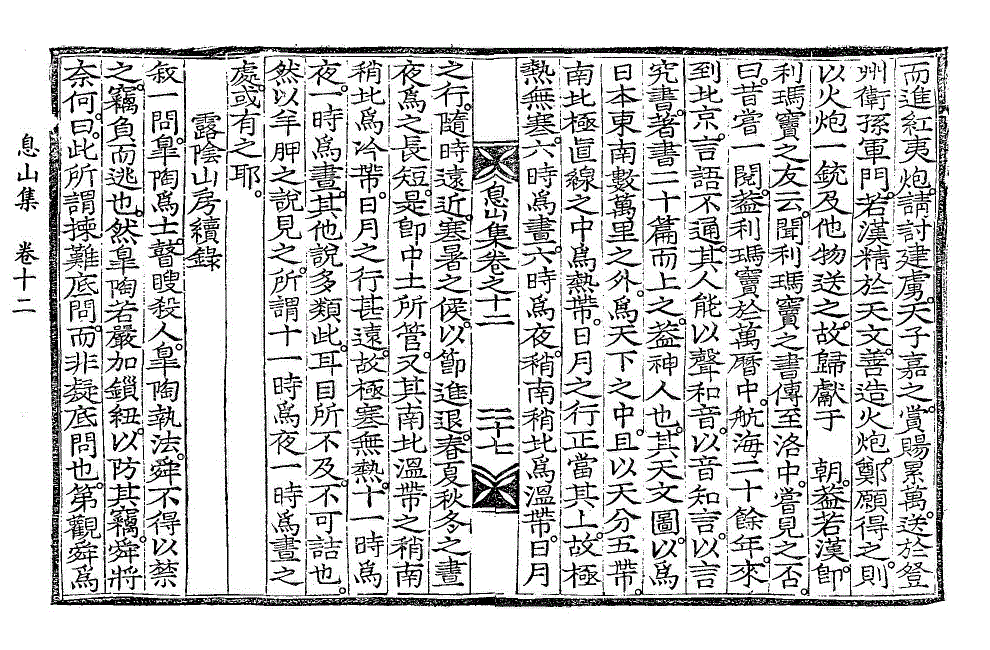 而进红夷炮。请讨建虏。天子嘉之。赏赐累万。送于登州卫孙军门。若汉精于天文。善造火炮。郑愿得之。则以火炮一铳及他物送之。故归献于 朝。盖若汉。即利玛窦之友云。闻利玛窦之书传至洛中。尝见之否。曰。昔尝一阅。盖利玛窦于万历中。航海二十馀年。来到北京。言语不通。其人能以声和音。以音知言。以言究书。著书二十篇而上之。盖神人也。其天文图。以为日本东南数万里之外。为天下之中。且以天分五带。南北极直线之中为热带。日月之行正当其上。故极热无寒。六时为昼。六时为夜。稍南稍北为温带。日月之行。随时远近。寒暑之候。以节进退。春夏秋冬之昼夜为之长短。是即中土所管。又其南北温带之稍南稍北为冷带。日月之行甚远。故极寒无热。十一时为夜。一时为昼。其他说多类此。耳目所不及。不可诘也。然以羊胛之说见之。所谓十一时为夜一时为昼之处。或有之耶。
而进红夷炮。请讨建虏。天子嘉之。赏赐累万。送于登州卫孙军门。若汉精于天文。善造火炮。郑愿得之。则以火炮一铳及他物送之。故归献于 朝。盖若汉。即利玛窦之友云。闻利玛窦之书传至洛中。尝见之否。曰。昔尝一阅。盖利玛窦于万历中。航海二十馀年。来到北京。言语不通。其人能以声和音。以音知言。以言究书。著书二十篇而上之。盖神人也。其天文图。以为日本东南数万里之外。为天下之中。且以天分五带。南北极直线之中为热带。日月之行正当其上。故极热无寒。六时为昼。六时为夜。稍南稍北为温带。日月之行。随时远近。寒暑之候。以节进退。春夏秋冬之昼夜为之长短。是即中土所管。又其南北温带之稍南稍北为冷带。日月之行甚远。故极寒无热。十一时为夜。一时为昼。其他说多类此。耳目所不及。不可诘也。然以羊胛之说见之。所谓十一时为夜一时为昼之处。或有之耶。露阴山房续录
叙一问。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皋陶执法。舜不得以禁之。窃负而逃也。然皋陶若严加锁纽。以防其窃。舜将奈何。曰。此所谓拣难底问。而非疑底问也。第观舜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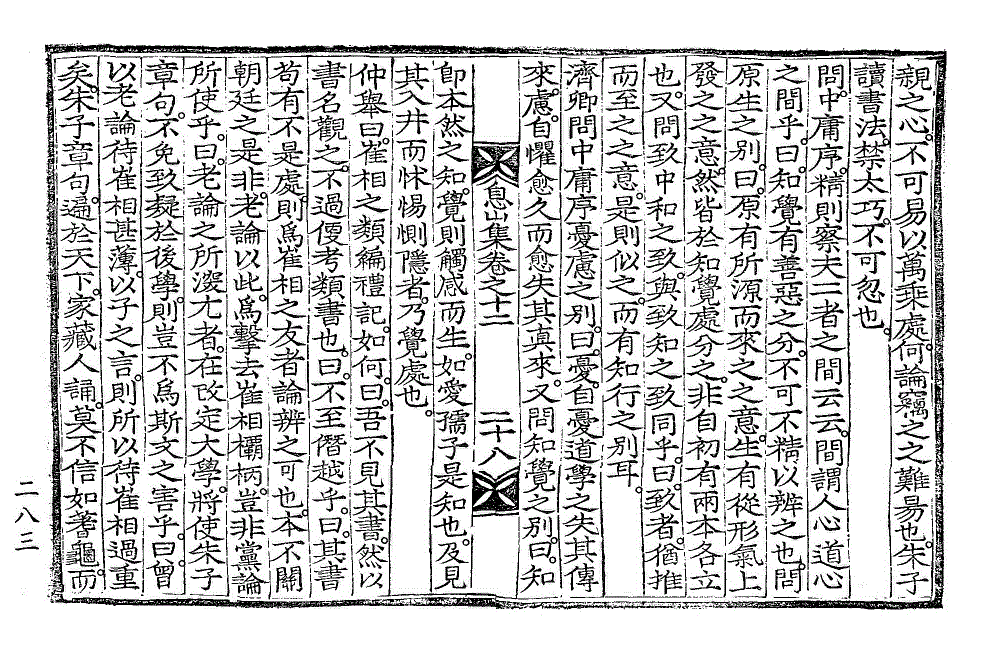 亲之心。不可易以万乘处。何论窃之之难易也。朱子读书法。禁太巧。不可忽也。
亲之心。不可易以万乘处。何论窃之之难易也。朱子读书法。禁太巧。不可忽也。问。中庸序。精则察夫二者之间云云。间谓人心道心之间乎。曰。知觉有善恶之分。不可不精以辨之也。问原生之别。曰。原有所源而来之之意。生有从形气上发之之意。然皆于知觉处分之。非自初有两本各立也。又问致中和之致。与致知之致同乎。曰。致者。犹推而至之之意。是则似之。而有知行之别耳。
济卿问中庸序忧虑之别。曰。忧。自忧道学之失其传来。虑。自惧愈久而愈失其真来。又问知觉之别。曰。知即本然之知。觉则触感而生。如爱孺子是知也。及见其入井而怵惕恻隐者。乃觉处也。
仲举曰。崔相之类编礼记。如何。曰。吾不见其书。然以书名观之。不过便考类书也。曰。不至僭越乎。曰。其书苟有不是处。则为崔相之友者论辨之可也。本不关朝廷之是非。老论以此。为击去崔相把柄。岂非党论所使乎。曰。老论之所深尤者。在改定大学。将使朱子章句。不免致疑于后学。则岂不为斯文之害乎。曰。曾以老论待崔相甚薄。以子之言。则所以待崔相过重矣。朱子章句。遍于天下。家藏人诵。莫不信如蓍龟。而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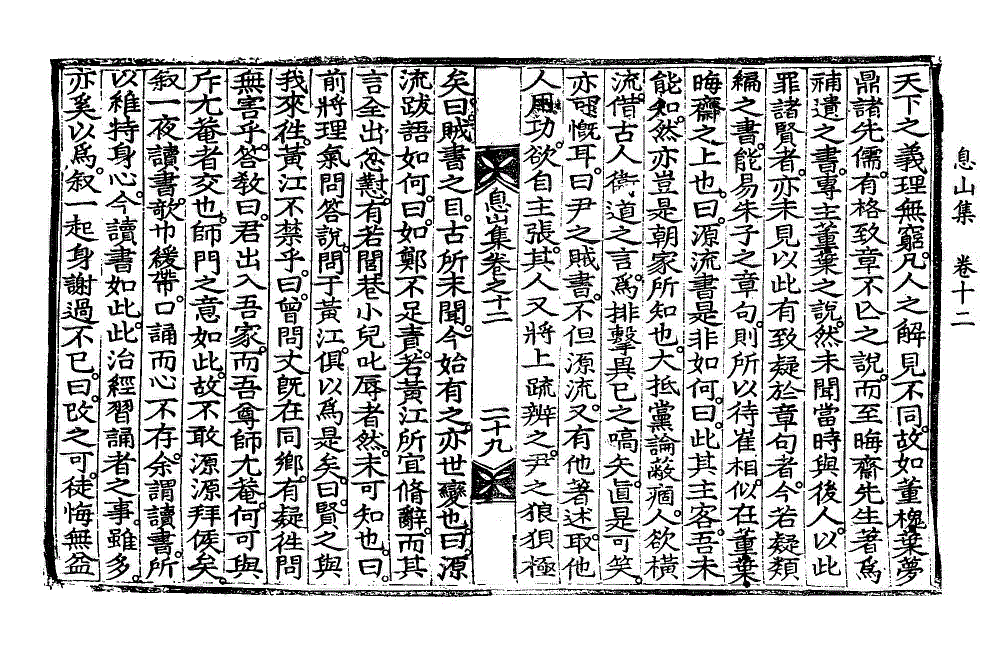 天下之义理无穷。凡人之解见不同。故如董槐,叶梦鼎诸先儒。有格致章不亡之说。而至晦斋先生著为补遗之书。专主董,叶之说。然未闻当时与后人。以此罪诸贤者。亦未见以此有致疑于章句者。今若疑类编之书。能易朱子之章句。则所以待崔相。似在董,叶,晦斋之上也。曰。源流书是非如何。曰。此其主客。吾未能知。然亦岂是朝家所知也。大抵党论蔽痼。人欲横流。借古人卫道之言。为排击异己之嗃矢。直是可笑。亦可慨耳。曰尹之贼书。不但源流。又有他著述。取他人用功。欲自主张。其人又将上疏辨之。尹之狼狈极矣。曰。贼书之目。古所未闻。今始有之。亦世变也。曰。源流跋语如何。曰。如郑不足责。若黄江所宜脩辞。而其言全出忿怼。有若闾巷小儿叱辱者然。未可知也。曰。前将理气问答说。问于黄江。俱以为是矣。曰。贤之与我来往。黄江不禁乎。曰。曾问丈既在同乡。有疑往问无害乎。答教曰。君出入吾家。而吾尊师尤庵。何可与斥尤庵者交也。师门之意如此。故不敢源源拜候矣。叙一夜读书。欹巾缓带。口诵而心不存。余谓读书。所以维持身心。今读书如此。此治经习诵者之事。虽多。亦奚以为。叙一起身谢过不已。曰。改之可。徒悔无益
天下之义理无穷。凡人之解见不同。故如董槐,叶梦鼎诸先儒。有格致章不亡之说。而至晦斋先生著为补遗之书。专主董,叶之说。然未闻当时与后人。以此罪诸贤者。亦未见以此有致疑于章句者。今若疑类编之书。能易朱子之章句。则所以待崔相。似在董,叶,晦斋之上也。曰。源流书是非如何。曰。此其主客。吾未能知。然亦岂是朝家所知也。大抵党论蔽痼。人欲横流。借古人卫道之言。为排击异己之嗃矢。直是可笑。亦可慨耳。曰尹之贼书。不但源流。又有他著述。取他人用功。欲自主张。其人又将上疏辨之。尹之狼狈极矣。曰。贼书之目。古所未闻。今始有之。亦世变也。曰。源流跋语如何。曰。如郑不足责。若黄江所宜脩辞。而其言全出忿怼。有若闾巷小儿叱辱者然。未可知也。曰。前将理气问答说。问于黄江。俱以为是矣。曰。贤之与我来往。黄江不禁乎。曰。曾问丈既在同乡。有疑往问无害乎。答教曰。君出入吾家。而吾尊师尤庵。何可与斥尤庵者交也。师门之意如此。故不敢源源拜候矣。叙一夜读书。欹巾缓带。口诵而心不存。余谓读书。所以维持身心。今读书如此。此治经习诵者之事。虽多。亦奚以为。叙一起身谢过不已。曰。改之可。徒悔无益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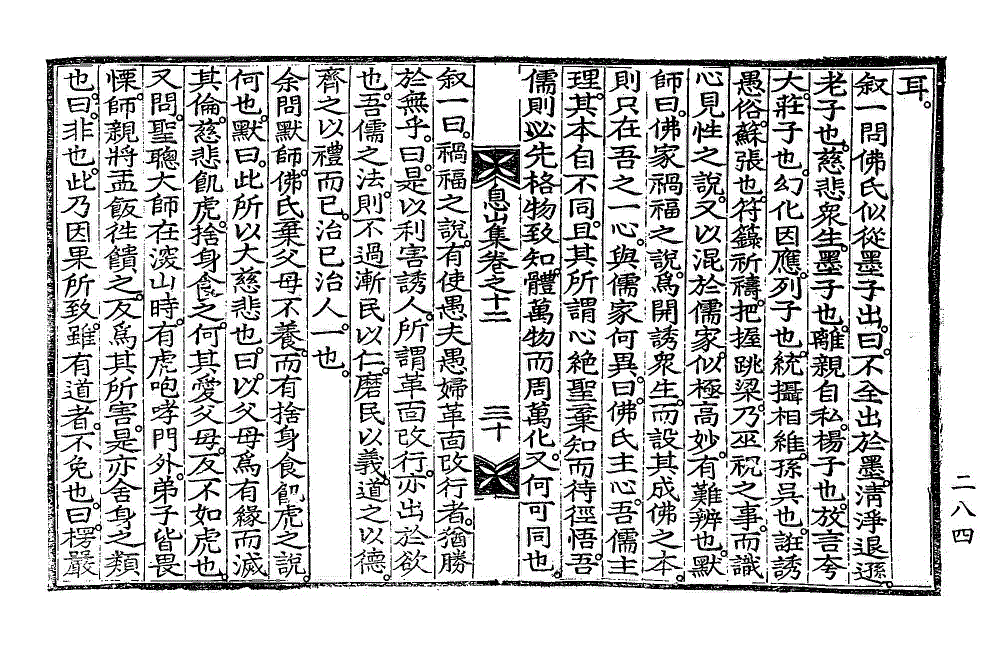 耳。
耳。叙一问佛氏似从墨子出。曰。不全出于墨。清净退逊。老子也。慈悲众生。墨子也。离亲自私。杨子也。放言夸大。庄子也。幻化因应。列子也。统摄相维。孙吴也。诳诱愚俗。苏张也。符箓祈祷。把握跳梁。乃巫祝之事。而识心见性之说。又以混于儒家。似极高妙。有难辨也。默师曰。佛家祸福之说。为开诱众生。而设其成佛之本。则只在吾之一心。与儒家何异。曰。佛氏主心。吾儒主理。其本自不同。且其所谓心绝圣弃知而待径悟。吾儒则必先格物致知。体万物而周万化。又何可同也。叙一曰。祸福之说。有使愚夫愚妇革面改行者。犹胜于无乎。曰。是以利害诱人。所谓革面改行。亦出于欲也。吾儒之法。则不过渐民以仁。磨民以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已。治己治人。一也。
余问默师。佛氏弃父母不养。而有舍身食饥虎之说。何也。默曰。此所以大慈悲也。曰。以父母为有缘而灭其伦。慈悲饥虎。舍身食之。何其爱父母。反不如虎也。又问。圣聪大师在深山时。有虎咆哮门外。弟子皆畏慄。师亲将盂饭往馈之。反为其所害。是亦舍身之类也。曰。非也。此乃因果所致。虽有道者。不免也。曰。楞严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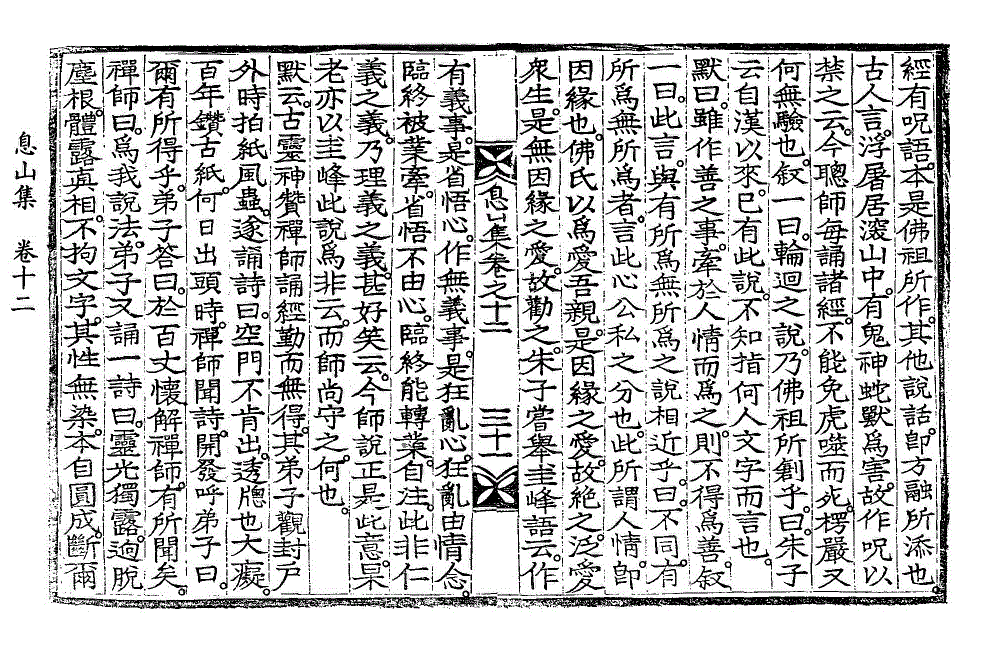 经有咒语。本是佛祖所作。其他说话。即方融所添也。古人言。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兽为害。故作咒以禁之云。今聪师每诵诸经。不能免虎噬而死。楞严又何无验也。叙一曰。轮回之说。乃佛祖所创乎。曰。朱子云自汉以来。已有此说。不知指何人文字而言也。
经有咒语。本是佛祖所作。其他说话。即方融所添也。古人言。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兽为害。故作咒以禁之云。今聪师每诵诸经。不能免虎噬而死。楞严又何无验也。叙一曰。轮回之说。乃佛祖所创乎。曰。朱子云自汉以来。已有此说。不知指何人文字而言也。默曰。虽作善之事。牵于人情而为之。则不得为善。叙一曰。此言。与有所为无所为之说相近乎。曰。不同。有所为无所为者。言此心公私之分也。此所谓人情。即因缘也。佛氏以为爱吾亲。是因缘之爱。故绝之。泛爱众生。是无因缘之爱。故劝之。朱子尝举圭峰语云。作有义事。是省悟心。作无义事。是狂乱心。狂乱由情念。临终被业牵。省悟不由心。临终能转业。自注。此非仁义之义。乃理义之义。甚好笑云。今师说正是此意。杲老亦以圭峰此说为非云。而师尚守之。何也。
默云。古灵神赞禅师诵经勤而无得。其弟子观封户外时拍纸风虫。遂诵诗曰。空门不肯出。透窗也大痴。百年钻古纸。何日出头时。禅师闻诗。开发呼弟子曰。尔有所得乎。弟子答曰。于百丈怀解禅师。有所闻矣。禅师曰。为我说法。弟子又诵一诗曰。灵光独露。迥脱尘根。体露真相。不拘文字。其性无染。本自圆成。断尔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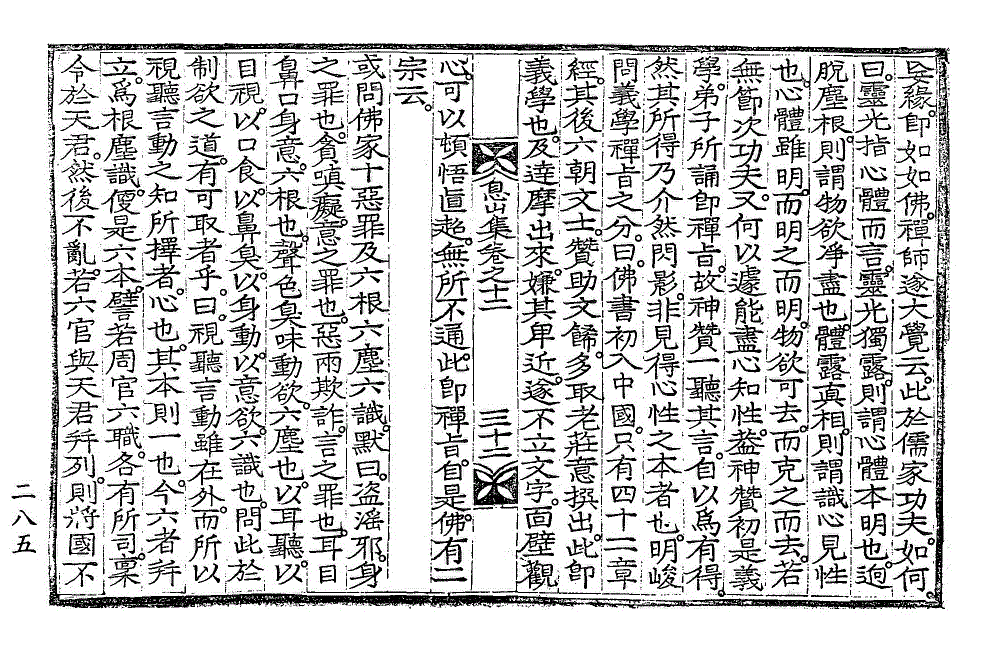 妄缘。即如如佛。禅师遂大觉云。此于儒家功夫。如何。曰。灵光指心体而言。灵光独露。则谓心体本明也。迥脱尘根。则谓物欲净尽也。体露真相。则谓识心见性也。心体虽明。而明之而明。物欲可去。而克之而去。若无节次功夫。又何以遽能尽心知性。盖神赞初是义学。弟子所诵即禅旨。故神赞一听其言。自以为有得。然其所得乃介然闪影。非见得心性之本者也。明峻问义学禅旨之分。曰。佛书初入中国。只有四十二章经。其后六朝文士。赞助文饰。多取老庄意撰出。此即义学也。及达摩出来。嫌其卑近。遂不立文字。面壁观心。可以顿悟直超。无所不通。此即禅旨。自是。佛有二宗云。
妄缘。即如如佛。禅师遂大觉云。此于儒家功夫。如何。曰。灵光指心体而言。灵光独露。则谓心体本明也。迥脱尘根。则谓物欲净尽也。体露真相。则谓识心见性也。心体虽明。而明之而明。物欲可去。而克之而去。若无节次功夫。又何以遽能尽心知性。盖神赞初是义学。弟子所诵即禅旨。故神赞一听其言。自以为有得。然其所得乃介然闪影。非见得心性之本者也。明峻问义学禅旨之分。曰。佛书初入中国。只有四十二章经。其后六朝文士。赞助文饰。多取老庄意撰出。此即义学也。及达摩出来。嫌其卑近。遂不立文字。面壁观心。可以顿悟直超。无所不通。此即禅旨。自是。佛有二宗云。或问佛家十恶罪及六根六尘六识。默曰。盗淫邪。身之罪也。贪嗔痴。意之罪也。恶两欺诈。言之罪也。耳目鼻口身意。六根也。声色臭味动欲。六尘也。以耳听。以目视。以口食。以鼻臭。以身动。以意欲。六识也。问此于制欲之道。有可取者乎。曰。视听言动虽在外。而所以视听言动之知所择者。心也。其本则一也。今六者并立。为根尘识。便是六本。譬若周官六职。各有所司。禀令于天君。然后不乱。若六官与天君并列。则将国不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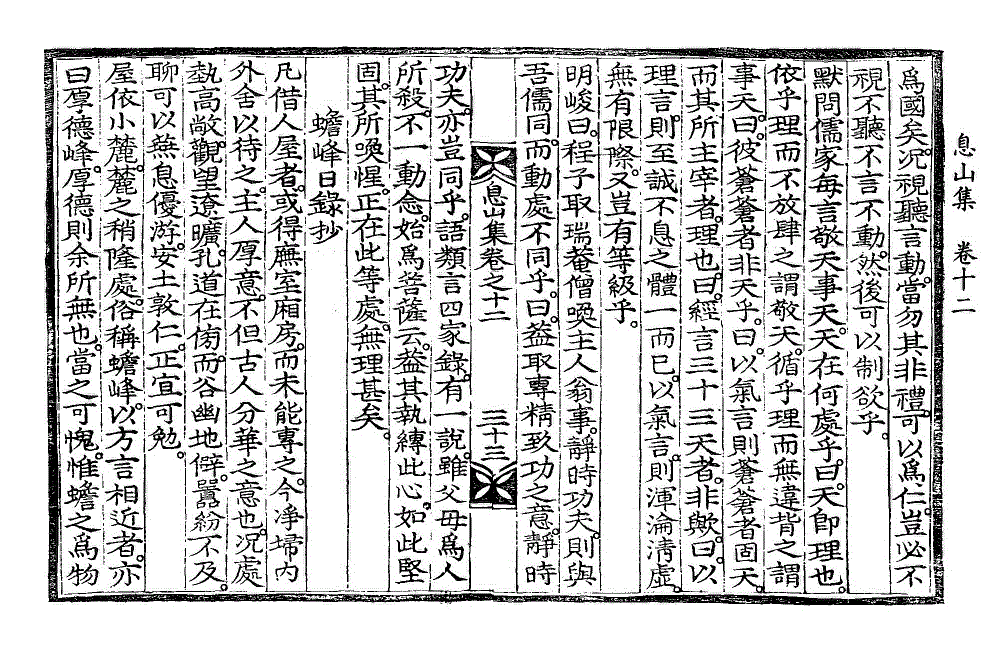 为国矣。况视听言动。当勿其非礼。可以为仁。岂必不视不听不言不动。然后可以制欲乎。
为国矣。况视听言动。当勿其非礼。可以为仁。岂必不视不听不言不动。然后可以制欲乎。默问儒家每言敬天事天。天在何处乎。曰。天即理也。依乎理而不放肆之谓敬天。循乎理而无违背之谓事天。曰。彼苍苍者非天乎。曰。以气言则苍苍者固天。而其所主宰者。理也。曰。经言三十三天者。非欤。曰。以理言。则至诚不息之体一而已。以气言。则浑沦清虚。无有限际。又岂有等级乎。
明峻曰。程子取瑞庵僧唤主人翁事。静时功夫。则与吾儒同。而动处不同乎。曰。盖取专精致功之意。静时功夫。亦岂同乎。语类言四家录。有一说。虽父母为人所杀。不一动念。始为菩萨云。盖其执縳此心。如此坚固。其所唤惺。正在此等处。无理甚矣。
蟾峰日录抄
凡借人屋者。或得庑室厢房。而未能专之。今净埽内外舍以待之。主人厚意。不但古人分华之意也。况处势高敞。观望辽旷。孔道在傍。而谷幽地僻。嚣纷不及。聊可以燕息优游。安土敦仁。正宜可勉。
屋依小麓。麓之稍隆处。俗称蟾峰。以方言相近者。亦曰厚德峰。厚德则余所无也。当之可愧。惟蟾之为物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6L 页
 顽而无能。污处而无求。与余迂拙似焉。遂于札牍幅面。书以蟾峰。
顽而无能。污处而无求。与余迂拙似焉。遂于札牍幅面。书以蟾峰。自蟾峰东出。迤而南复隆峙。其顶可搆一区小亭。亦姜氏别业。未暇屋之者也。步屧往临。下有立岩。势甚陡绝。鉴湖一带。横前数十里。绿野清流。尽入膝下。盘桓眺望。久而忘归。
阶上海棠正开。紫腻可爱。傍有数丛菊。久旱枝叶憔悴。人情例多取近而忽远。即此观之。孰不重棠而轻菊也。凡君子抱德不显。处于陋巷。而鄙夫凡流。若纡青拖紫。荣宠一时。则人之趋舍。亦何以异夫看花乎。于是命奚日浇。菊丛渐看稣茂。凌霜吐艳。会有其时。国家培养人才。盍观于是哉。
金泉。有酒泉之号。以所酿过夏。酒甘冽殊美故也。闻酿酒之水有三井。二在邮村。一在蟾峰。余所寓之前邮村之井。一为潦水填塞。今则只有一焉。若不用此水。则酒味不能十分佳。故金陵宰。亦借邮丞而得之。水性之不同。亦如此。
游诚之曰。方其寂然无事。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此言似善形容。而有所未然。无极而太极云者。谓无所极而有所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7H 页
 极也。太极本无极者。谓有所极者。本是无所极也。故论无极太极。当于太极上。拈出其无所极之意。不可曰。如是为无极。如彼为太极。
极也。太极本无极者。谓有所极者。本是无所极也。故论无极太极。当于太极上。拈出其无所极之意。不可曰。如是为无极。如彼为太极。易传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近思余无可观之变可玩之占。正宜观其象玩其辞。此难与众人言也。
日晕两珥。占曰。有谋反者。日晕四珥。占曰。将亡有反者。日晕璚。占曰。君臣乖离。臣有外心。其国兵起。有逃臣。白虹贯日。占曰。近臣有为乱者。日旁有四五虹交贯日。占曰。所临之地流血。两军相当。从上击下。大胜。今日晕五虹并出。而二虹交贯日。不知为何占。恭惟我 新王继统。圣德夙彰。邦人方颙望至治。仁爱之天。何繇而示警若此也。漆室之忧。可胜言乎。
散策上蟾峰北望。黄岳穹然。此湖岭之际一大山也。直旨川出自其中东南来。与鉴水合。南望伽倻列岫。峭拔云里。亦可以时叙幽郁也。
自金泉遵鉴水南行二十里。有装岩村。又转而西上不数里。有所谓道岩。极有溪山幽致。三休堂姜公来游其上。欲构亭居之。未久公北谪。殁于谪所。故未果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