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书
书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7H 页
 与罗浮全丈
与罗浮全丈日间辱临。多荷。区区所陈。幸无呵责。几择乎刍荛者也。甚盛甚盛。第念积年疑阻。一朝拔去。诚亦未易。敢复毕其说焉。凡丈与赵友相失。实因中间交搆之言。言之者。固小人之事。听之者。有不可咎。盖彼方罹大祸。以死生为虑。而云云之说。得投其间。夫以曾母之贤。曾子之孝。而犹投杼于三至之言。两家之谊虽厚。困极易憾。乃人之情。赵友安得不动。平心徐究。则赵友之不平于丈。容有其由。丈之自阻于赵友。不亦太过乎。然此已往之事。置之不言。惟今春乡约一事。复出于意外。弟作驳通。兄恣诋诟。彼以年少。失待丈之义。丈之退坐。不欲同约。宜矣。虽然。洞邻之义。因此乖戾。乡约之法。因此废坏。分朋攻击。互相诽谤。气象愁惨。此何事也。此何举也。极为寒心。不佞于乡约兴废。无所相关。但有爱礼之心也。至于丈与他世居之人。必不以累世从事之所乐于废罢。而犹不思所以改图。则非所望于长者也。岂不以乡约虽重。吾之见侮于人如此。何可苟自求解乎。此有不然者。两家所嫌。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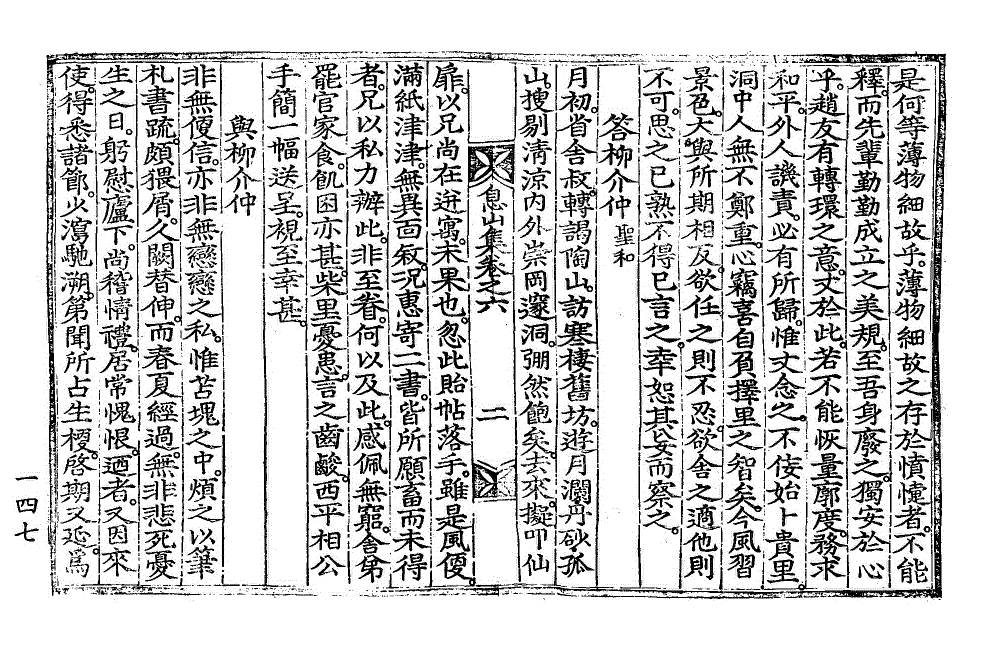 是何等薄物细故乎。薄物细故之存于愤懥者。不能释。而先辈勤勤成立之美规。至吾身废之。独安于心乎。赵友有转环之意。丈于此。若不能恢量廓度。务求和平。外人讥责。必有所归。惟丈念之。不佞始卜贵里。洞中人无不郑重。心窃喜自负择里之智矣。今风习景色。大与所期相反。欲任之则不忍。欲舍之适他则不可。思之已熟不得已言之。幸恕其妄而察之。
是何等薄物细故乎。薄物细故之存于愤懥者。不能释。而先辈勤勤成立之美规。至吾身废之。独安于心乎。赵友有转环之意。丈于此。若不能恢量廓度。务求和平。外人讥责。必有所归。惟丈念之。不佞始卜贵里。洞中人无不郑重。心窃喜自负择里之智矣。今风习景色。大与所期相反。欲任之则不忍。欲舍之适他则不可。思之已熟不得已言之。幸恕其妄而察之。答柳介仲(圣和)
月初。省舍叔。转谒陶山。访寒栖旧坊。游月澜,丹砂,孤山。搜剔清凉内外崇冈邃洞。弸然饱矣。去来。拟叩仙扉。以兄尚在迸寓。未果也。忽此贻帖落手。虽是风便。满纸津津。无异面叙。况惠寄二书。皆所愿畜而未得者。兄以私力办此。非至眷。何以及此。感佩无穷。舍弟罢官家食。饥困亦甚。柴里忧患。言之齿
与柳介仲
非无便信。亦非无恋恋之私。惟苫块之中。烦之以笔札书疏。颇猥屑。久阙替伸。而春夏经过。无非悲死忧生之日。躬慰庐下。尚稽情礼。居常愧恨。乃者。又因来使。得悉诸节。少泻驰溯。第闻所占生梗。启期又延。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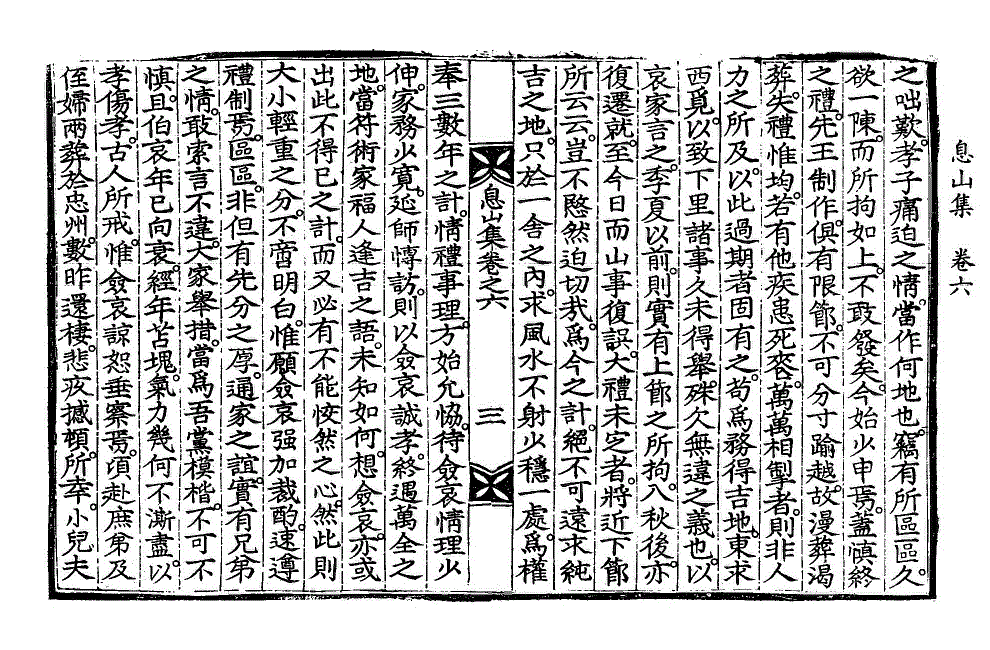 之咄叹。孝子痛迫之情。当作何地也。窃有所区区。久欲一陈。而所拘如上。不敢发矣。今始少申焉。盖慎终之礼。先王制作。俱有限节。不可分寸踰越。故漫葬渴葬。失礼惟均。若有他疾患死丧。万万相掣者。则非人力之所及。以此过期者固有之。苟为务得吉地。东求西觅。以致下里诸事久未得举。殊欠无违之义也。以哀家言之。季夏以前。则实有上节之所拘。入秋后。亦复迁就。至今日而山事复误。大礼未定者。将近下节所云云。岂不悯然迫切哉。为今之计。绝不可远求纯吉之地。只于一舍之内。求风水不射少稳一处。为权奉三数年之计。情礼事理。方始允协。待佥哀情理少伸。家务少宽。延师博访。则以佥哀诚孝。终遇万全之地。当符术家福人逢吉之语。未知如何。想佥哀。亦或出此不得已之计。而又必有不能恔然之心。然此则大小轻重之分。不啻明白。惟愿佥哀强加裁酌。速遵礼制焉。区区。非但有先分之厚。通家之谊。实有兄弟之情。敢索言不违。大家举措。当为吾党模楷。不可不慎。且伯哀年已向衰。经年苫块。气力几何不澌尽。以孝伤孝。古人所戒。惟佥哀谅恕垂察焉。顷赴庶弟及侄妇两葬于忠州。数昨还栖。悲疚撼顿。所幸。小儿夫
之咄叹。孝子痛迫之情。当作何地也。窃有所区区。久欲一陈。而所拘如上。不敢发矣。今始少申焉。盖慎终之礼。先王制作。俱有限节。不可分寸踰越。故漫葬渴葬。失礼惟均。若有他疾患死丧。万万相掣者。则非人力之所及。以此过期者固有之。苟为务得吉地。东求西觅。以致下里诸事久未得举。殊欠无违之义也。以哀家言之。季夏以前。则实有上节之所拘。入秋后。亦复迁就。至今日而山事复误。大礼未定者。将近下节所云云。岂不悯然迫切哉。为今之计。绝不可远求纯吉之地。只于一舍之内。求风水不射少稳一处。为权奉三数年之计。情礼事理。方始允协。待佥哀情理少伸。家务少宽。延师博访。则以佥哀诚孝。终遇万全之地。当符术家福人逢吉之语。未知如何。想佥哀。亦或出此不得已之计。而又必有不能恔然之心。然此则大小轻重之分。不啻明白。惟愿佥哀强加裁酌。速遵礼制焉。区区。非但有先分之厚。通家之谊。实有兄弟之情。敢索言不违。大家举措。当为吾党模楷。不可不慎。且伯哀年已向衰。经年苫块。气力几何不澌尽。以孝伤孝。古人所戒。惟佥哀谅恕垂察焉。顷赴庶弟及侄妇两葬于忠州。数昨还栖。悲疚撼顿。所幸。小儿夫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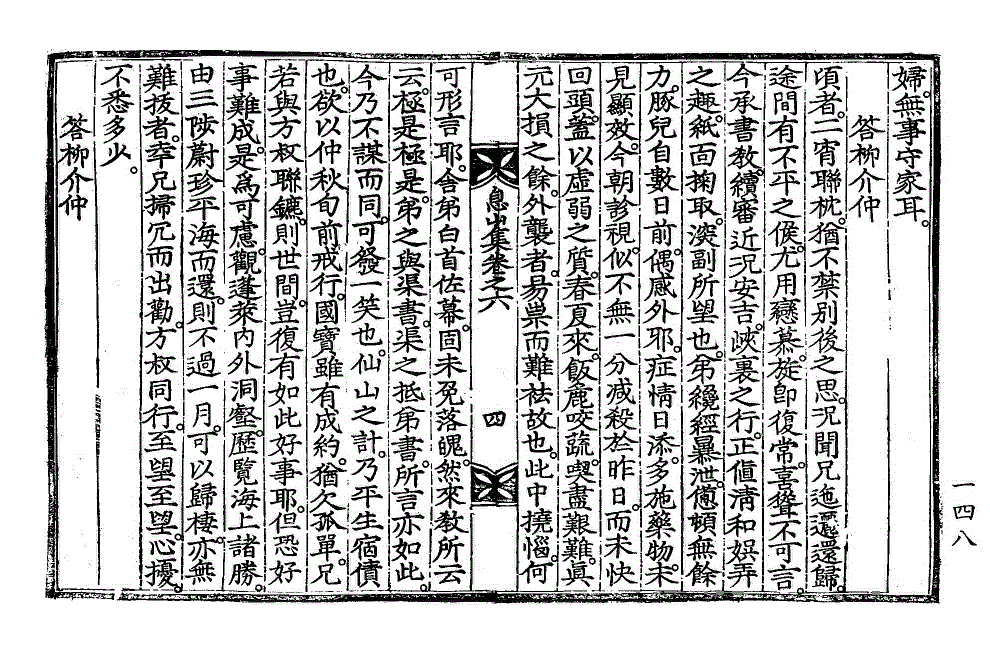 妇。无事守家耳。
妇。无事守家耳。答柳介仲
顷者。二宵联枕。犹不禁别后之思。况闻兄迤逦还归。途间有不平之候。尤用恋慕。旋即复常。喜耸不可言。今承书教。续审近况安吉。峡里之行。正值清和娱弄之趣。纸面掬取。深副所望也。弟才经㬥泄。惫顿无馀力。豚儿自数日前。偶感外邪。症情日添。多施药物。未见显效。今朝诊视。似不无一分减杀于昨日。而未快回头。盖以虚弱之质。春夏来。饭粗咬蔬。吃尽艰难。真元大损之馀。外袭者。易祟而难袪故也。此中挠恼。何可形言耶。舍弟白首佐幕。固未免落魄。然来教所云云。极是极是。弟之与渠书。渠之抵弟书。所言亦如此。今乃不谋而同。可发一笑也。仙山之计。乃平生宿债也。欲以仲秋旬前戒行。国宝虽有成约。犹欠孤单。兄若与方叔联镳。则世间。岂复有如此好事耶。但恐好事难成。是为可虑。观蓬莱内外洞壑。历览海上诸胜。由三陟蔚珍平海而还。则不过一月。可以归栖。亦无难拔者。幸兄扫冗而出劝。方叔同行。至望至望。心扰。不悉多少。
答柳介仲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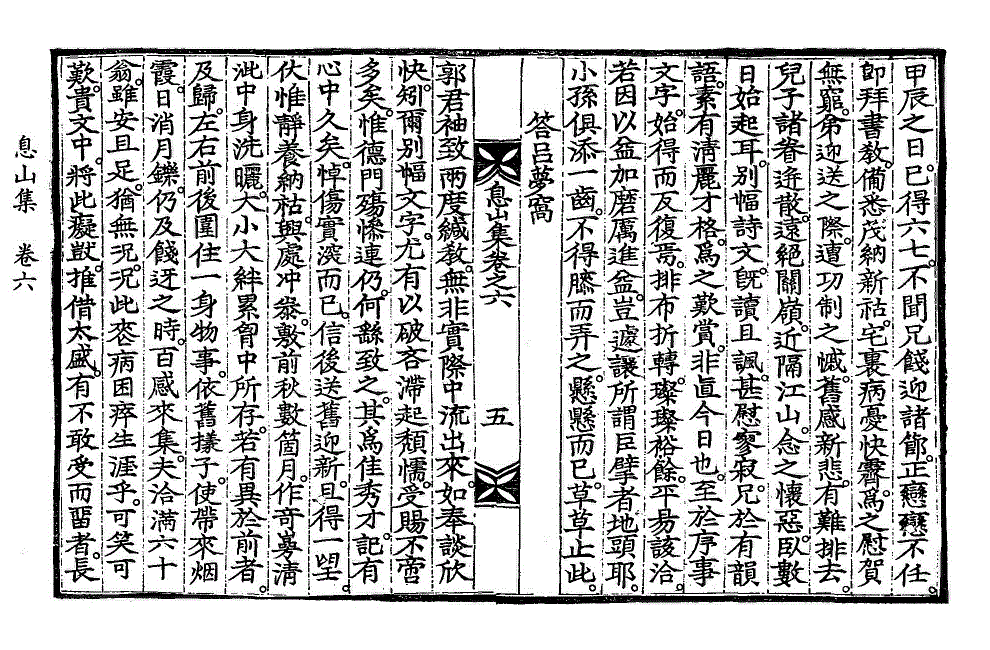 甲辰之日。已得六七。不闻兄饯迎诸节。正恋恋不任。即拜书教。备悉茂纳新祜。宅里病忧快霁。为之慰贺无穷。弟迎送之际。遭功制之戚。旧感新悲。有难排去。儿子诸眷迸散。远绝关岭。近隔江山。念之怀恶。卧数日始起耳。别幅诗文。既读且讽。甚慰寥寂。兄于有韵语。素有清丽才格。为之叹赏。非直今日也。至于序事文字。始得而反复焉。排布折转。璨璨裕馀。平易该洽。若因以益加磨厉进益。岂遽让所谓巨擘者地头耶。小孙俱添一齿。不得膝而弄之。悬悬而已。草草止此。
甲辰之日。已得六七。不闻兄饯迎诸节。正恋恋不任。即拜书教。备悉茂纳新祜。宅里病忧快霁。为之慰贺无穷。弟迎送之际。遭功制之戚。旧感新悲。有难排去。儿子诸眷迸散。远绝关岭。近隔江山。念之怀恶。卧数日始起耳。别幅诗文。既读且讽。甚慰寥寂。兄于有韵语。素有清丽才格。为之叹赏。非直今日也。至于序事文字。始得而反复焉。排布折转。璨璨裕馀。平易该洽。若因以益加磨厉进益。岂遽让所谓巨擘者地头耶。小孙俱添一齿。不得膝而弄之。悬悬而已。草草止此。答吕梦窝
郭君袖致两度缄教。无非实际中流出来。如奉谈欣快。矧尔别幅文字。尤有以破吝滞起颓懦。受赐不啻多矣。惟德门殇惨连仍。何繇致之。其为佳秀才。记有心中久矣。悼伤实深而已。信后送旧迎新。且得一望。伏惟静养纳祜。兴处冲泰。敷前秋数个月。作奇崿清泚中身洗晒。大小大绊累胸中所存。若有异于前者。及归。左右前后围住一身物事。依旧㨾子。使带来烟霞。日消月铄。仍及饯迓之时。百感来集。夫洽满六十翁。虽安且足。犹无况。况此丧病困瘁生涯乎。可笑可叹。贵文中。将此痴呆。推借太盛。有不敢受而留者。长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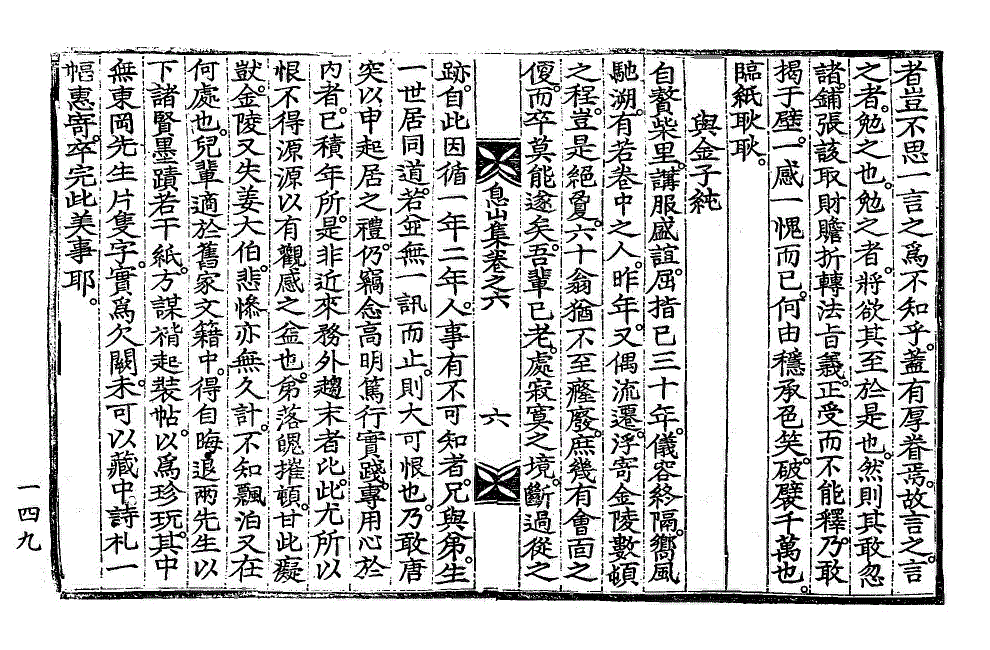 者岂不思一言之为不知乎。盖有厚眷焉。故言之。言之者。勉之也。勉之者。将欲其至于是也。然则其敢忽诸。铺张该取财赡折转法旨义。正受而不能释。乃敢揭于壁。一感一愧而已。何由稳承色笑。破襞千万也。临纸耿耿。
者岂不思一言之为不知乎。盖有厚眷焉。故言之。言之者。勉之也。勉之者。将欲其至于是也。然则其敢忽诸。铺张该取财赡折转法旨义。正受而不能释。乃敢揭于壁。一感一愧而已。何由稳承色笑。破襞千万也。临纸耿耿。与金子纯
自赘柴里。讲服盛谊。屈指已三十年。仪容终隔。向风驰溯。有若卷中之人。昨年。又偶流迁。浮寄金陵数顿之程。岂是绝夐。六十翁犹不至癃废。庶几有会面之便。而卒莫能遂矣。吾辈已老。处寂寞之境。断过从之迹。自此因循一年二年。人事有不可知者。兄与弟。生一世居同道。若并无一讯而止。则大可恨也。乃敢唐突以申起居之礼。仍窃念高明笃行实践。专用心于内者。已积年所。是非近来务外趋末者比。此尤所以恨不得源源以有观感之益也。弟落魄摧顿。甘此痴呆。金陵又失姜大伯。悲惨亦无久计。不知飘泊又在何处也。儿辈适于旧家文籍中。得自晦,退两先生以下诸贤墨迹若干纸。方谋褙起装帖。以为珍玩。其中无东冈先生片只字。实为欠阙。未可以藏中。诗札一幅惠寄。卒完此美事耶。
答李知守
恋承近问。凡百佳胜。慰泻慰泻。垂问所读之书。六经孰非学者所可读。而以程朱所教。则不无先后缓急。左右亦岂不知耶。左右读诸经略尽。而率皆汎滥不切。当更从头至尾。益加整理。用究竟法可也。然则窃谓莫先于大学一部。须大段著力。期至洞澈烂熟。更无可读者。然后方可易他书看也。如何如何。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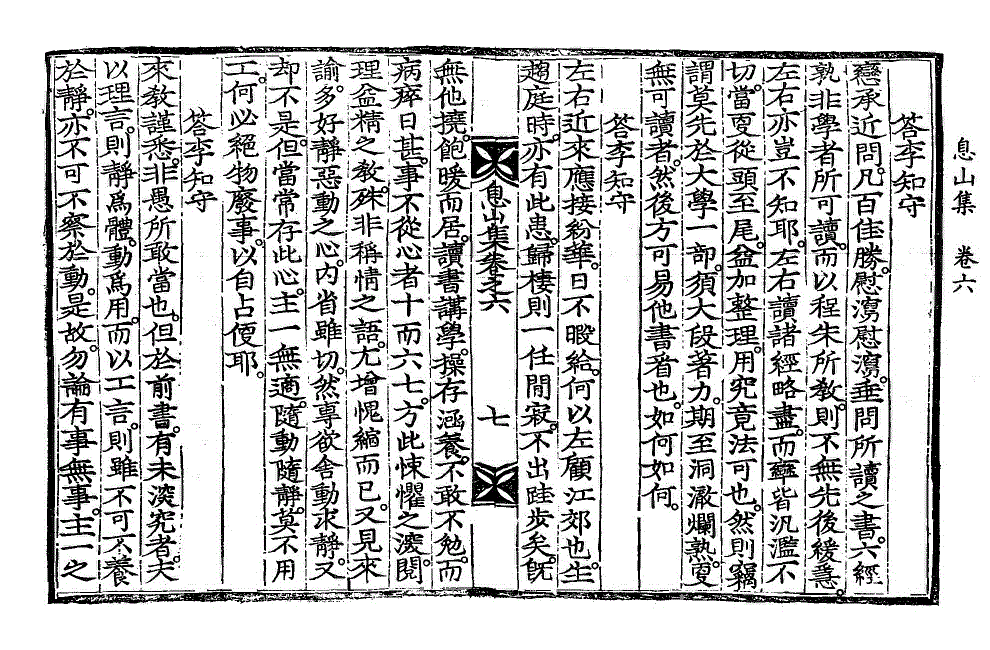 答李知守
答李知守左右近来应接纷华。日不暇给。何以左顾江郊也。生趋庭时。亦有此患。归栖则一任閒寂。不出跬步矣。既无他挠。饱暖而居。读书讲学。操存涵养。不敢不勉。而病瘁日甚。事不从心者十而六七。方此悚惧之深。阅理益精之教。殊非称情之语。尤增愧缩而已。又见来谕。多好静恶动之心。内省虽切。然专欲舍动求静。又却不是。但当常存此心。主一无适。随动随静。莫不用工。何必绝物废事。以自占便耶。
答李知守
来教谨悉。非愚所敢当也。但于前书。有未深究者。夫以理言。则静为体。动为用。而以工言。则虽不可不养于静。亦不可不察于动。是故。勿论有事无事。主一之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0L 页
 工不间断。则心地自然莹净。无适不一。外物岂足为之累哉。愚言好静恶动者。非谓知守以此为务。所谓恶长动无静之心。著在方寸地。转成病根。不觉为舍动求静之偏故云也。且以所引朱子说言之。既曰动处求之。则有意求免乎静之一偏。而反倚乎动之一偏。则独不曰静处求之。则有意求免乎动之一偏。而反倚乎静之一偏乎。其所为而言者异。则言亦不同。其实谓不可倚于一偏也。如何如何。
工不间断。则心地自然莹净。无适不一。外物岂足为之累哉。愚言好静恶动者。非谓知守以此为务。所谓恶长动无静之心。著在方寸地。转成病根。不觉为舍动求静之偏故云也。且以所引朱子说言之。既曰动处求之。则有意求免乎静之一偏。而反倚乎动之一偏。则独不曰静处求之。则有意求免乎动之一偏。而反倚乎静之一偏乎。其所为而言者异。则言亦不同。其实谓不可倚于一偏也。如何如何。答李知守
诚敬论。举世非之。非但李公之著说也。天道微妙。非初学所可窥测。亦非所可论说。然天人一理。若反诸其心。而推其自然之本体。则亦岂无可默识之道也。元气游气说。大槩得之。道器说多可疑。凡天地万物。莫非器也。而一物之中。有为此物之则者。道也。其在人则日用之事亦器。而其当然之则。道也。是以脩其事。所以明其道也。故曰。下学而上达。来说云。道者。超乎事物而人所当行之理。器者。由乎事物而人所著力之处。如此则事物之外。别有器。而器与道又不相关摄。人之用工。亦有二涂也。程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虽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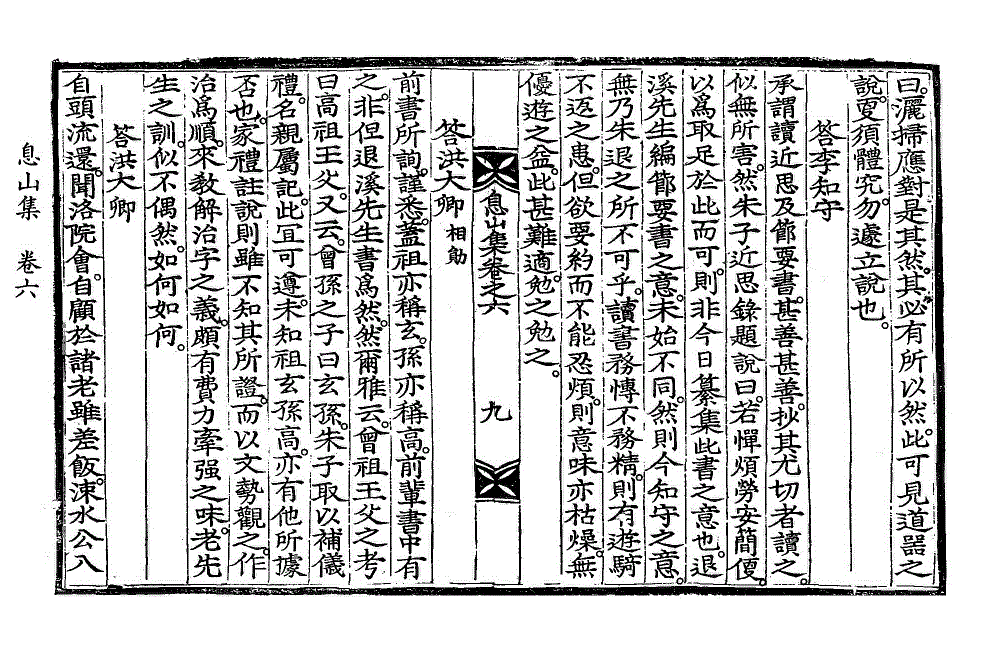 曰。洒扫应对是其然。其必有所以然。此可见道器之说。更须体究。勿遽立说也。
曰。洒扫应对是其然。其必有所以然。此可见道器之说。更须体究。勿遽立说也。答李知守
承谓读近思及节要书。甚善甚善。抄其尤切者读之。似无所害。然朱子近思录题说曰。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纂集此书之意也。退溪先生编节要书之意。未始不同。然则今知守之意。无乃朱退之所不可乎。读书务博不务精。则有游骑不返之患。但欲要约而不能忍烦。则意味亦枯燥。无优游之益。此甚难适。勉之勉之。
答洪大卿(相勋)
前书所询。谨悉。盖祖亦称玄。孙亦称高。前辈书中有之。非但退溪先生书为然。然尔雅云。曾祖王父之考曰高祖王父。又云。曾孙之子曰玄孙。朱子取以补仪礼。名亲属记。此宜可遵。未知祖玄孙高。亦有他所据否也。家礼注说则虽不知其所證。而以文势观之。作治为顺。来教解治字之义。颇有费力牵强之味。老先生之训。似不偶然。如何如何。
答洪大卿
自头流还。闻洛院会。自顾于诸老虽差饭。涑水公入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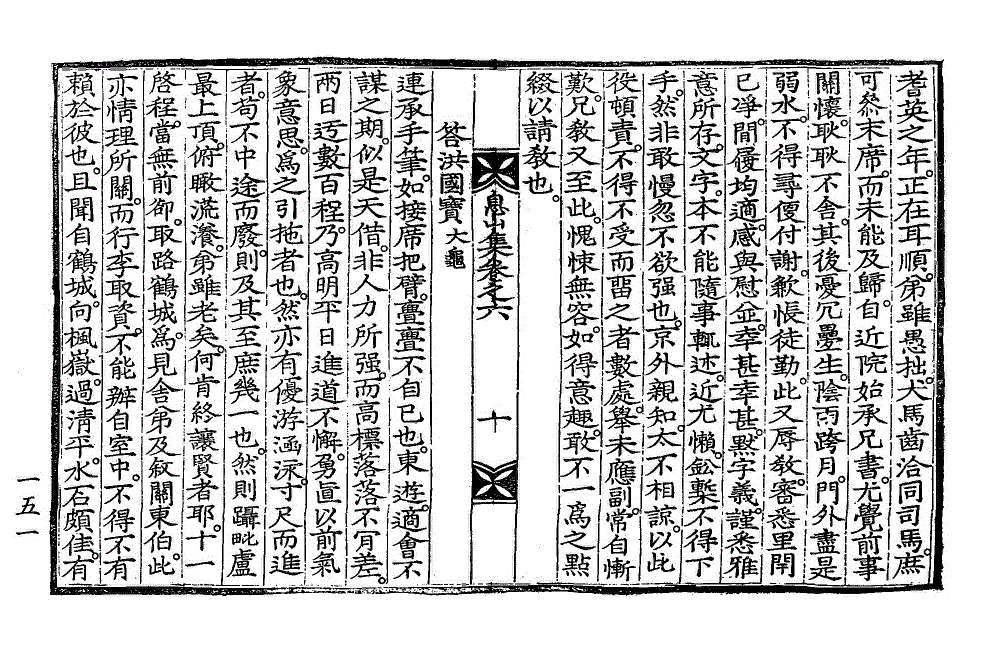 耆英之年。正在耳顺。弟虽愚拙。犬马齿洽同司马。庶可参末席。而未能及归。自近院始承兄书。尤觉前事关怀。耿耿不舍。其后忧冗叠生。阴雨跨月。门外尽是弱水。不得寻便付谢。歉怅徒勤。此又辱教。审悉里闬已净。閒履均适。感与慰并。幸甚幸甚。默字义。谨悉雅意所存。文字。本不能随事辄述。近尤懒。铅椠不得下手。然非敢慢忽不欲强也。京外亲知。太不相谅。以此役顿责。不得不受而留之者数处。举未应副。常自惭叹。兄教又至此。愧悚无容。如得意趣。敢不一为之点缀以请教也。
耆英之年。正在耳顺。弟虽愚拙。犬马齿洽同司马。庶可参末席。而未能及归。自近院始承兄书。尤觉前事关怀。耿耿不舍。其后忧冗叠生。阴雨跨月。门外尽是弱水。不得寻便付谢。歉怅徒勤。此又辱教。审悉里闬已净。閒履均适。感与慰并。幸甚幸甚。默字义。谨悉雅意所存。文字。本不能随事辄述。近尤懒。铅椠不得下手。然非敢慢忽不欲强也。京外亲知。太不相谅。以此役顿责。不得不受而留之者数处。举未应副。常自惭叹。兄教又至此。愧悚无容。如得意趣。敢不一为之点缀以请教也。答洪国宝(大龟)
连承手笔。如接席把臂。亹亹不自已也。东游。适会不谋之期。似是天借。非人力所强。而高标落落不肯差。两日迂数百程。乃高明平日进道不懈。勇直以前气象意思。为之引拖者也。然亦有优游涵泳。寸尺而进者。苟不中途而废。则及其至庶几一也。然则蹑毗卢最上顶。俯瞰𣺬瀁。弟虽老矣。何肯终让贤者耶。十一启程。当无前却。取路鹤城。为见舍弟及叙关东伯。此亦情理所关。而行李取资。不能办自室中。不得不有赖于彼也。且闻自鹤城。向枫岳。过清平。水石颇佳。有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2H 页
 高丽处士李资贤遗躅。历访挹仰。自来所期。趁枫叶正酣。当抵长安。似在晦初也。兄若直走堤宁间。入山必在吾先。幸少相须于某处。作我迷道指南。必欲耽进务先。愿分留风云物色。使我追拾零尘。毋徒尽取以去也。临风一笑。不任怅然而已。
高丽处士李资贤遗躅。历访挹仰。自来所期。趁枫叶正酣。当抵长安。似在晦初也。兄若直走堤宁间。入山必在吾先。幸少相须于某处。作我迷道指南。必欲耽进务先。愿分留风云物色。使我追拾零尘。毋徒尽取以去也。临风一笑。不任怅然而已。答洪国宝
入山。自长安至榆岾。问兄行色。遇入定。行脚无阙焉。然终不得影响。虎溪一笑。虽未得同。鸾背吹笙。亦难得闻矣。归来耿耿在心。忽承惠幅。审已还税。清裕何等慰畅。想所得既富。未知长得几许韵格也。通川邂逅。殊是不易。弟仍入京。终未蹑海岸。老叔超然独往。乃与兄投际于逆旅。人事不可定者如此。游录。果有所乱笔者。归栖后。依旧入冗累坑中。愦愦度无暇及此。如得修整得脱。可不一出以證于贵录。为一笑也。弟之无得于兄。与兄无异。而兄先俯索。亦堪愧叹。劳惫仅草。
与李和叔
天地秋矣。足下静履状。伏惟清茂。弊陋愿交于足下。非一日之积。时省家叔。高寓接闬。声光密迩。倾盖而吐露。非无便也。惟是骨肉聚散。每患猝剧。且坐颓懒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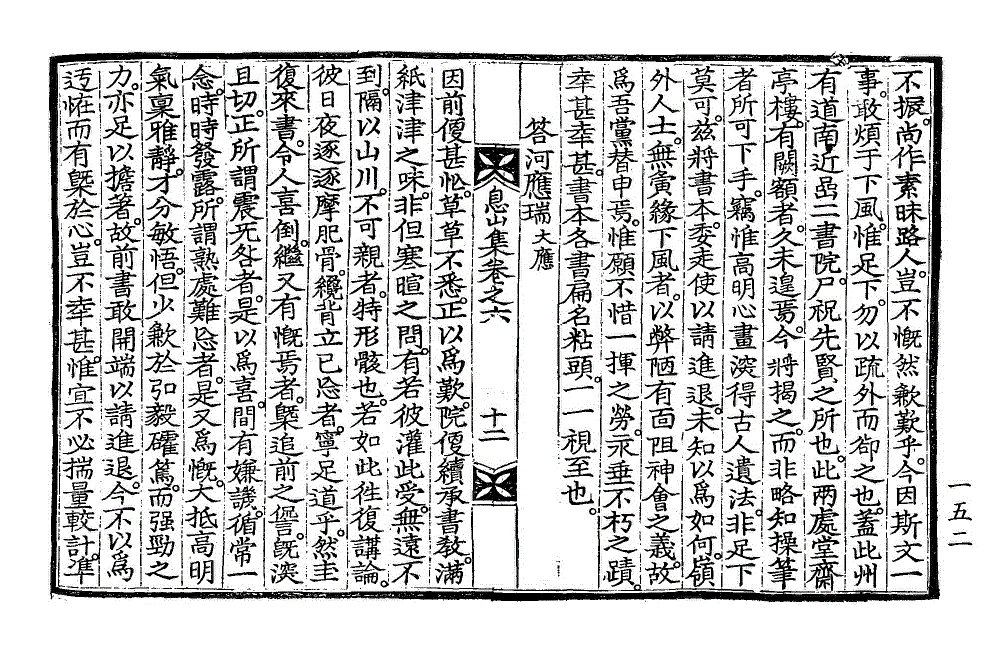 不振。尚作素昧路人。岂不慨然歉叹乎。今因斯文一事。敢烦于下风。惟足下。勿以疏外而却之也。盖此州有道南,近岩二书院。尸祝先贤之所也。此两处堂斋亭楼。有阙额者。久未遑焉。今将揭之。而非略知操笔者所可下手。窃惟高明心画深得古人遗法。非足下莫可。玆将书本。委走使以请进退。未知以为如何。岭外人士。无夤缘下风者。以弊陋有面阻神会之义。故为吾党替申焉。惟愿不惜一挥之劳。永垂不朽之迹。幸甚幸甚。书本各书扁名粘头。一一视至也。
不振。尚作素昧路人。岂不慨然歉叹乎。今因斯文一事。敢烦于下风。惟足下。勿以疏外而却之也。盖此州有道南,近岩二书院。尸祝先贤之所也。此两处堂斋亭楼。有阙额者。久未遑焉。今将揭之。而非略知操笔者所可下手。窃惟高明心画深得古人遗法。非足下莫可。玆将书本。委走使以请进退。未知以为如何。岭外人士。无夤缘下风者。以弊陋有面阻神会之义。故为吾党替申焉。惟愿不惜一挥之劳。永垂不朽之迹。幸甚幸甚。书本各书扁名粘头。一一视至也。答河应瑞(大应)
因前便甚忙。草草不悉。正以为叹。院便续承书教。满纸津津之味。非但寒暄之问。有若彼灌此受。无远不到。隔以山川。不可亲者。特形骸也。若如此往复讲论。彼日夜逐逐摩肌骨。才背立已忘者。宁足道乎。然圭复来书。令人喜倒。继又有慨焉者。槩追前之愆。既深且切。正所谓震无咎者。是以为喜。间有嫌讥。循常一念。时时发露。所谓熟处难忘者。是又为慨。大抵高明气禀雅静。才分敏悟。但少歉于弘毅礭笃。而强劲之力。亦足以担著。故前书敢开端以请进退。今不以为迂怪而有槩于心。岂不幸甚。惟宜不必揣量较计。准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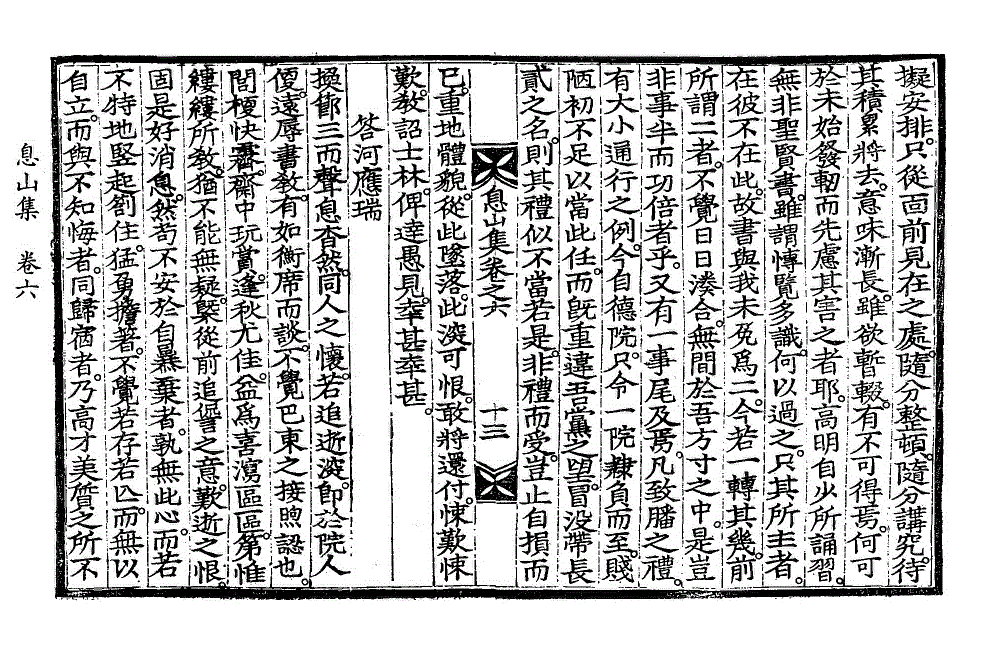 拟安排。只从面前见在之处。随分整顿。随分讲究。待其积累将去。意味渐长。虽欲暂辍。有不可得焉。何可于未始发轫而先虑其害之者耶。高明自少所诵习。无非圣贤书。虽谓博览多识。何以过之。只其所主者。在彼不在此。故书与我未免为二。今若一转其几。前所谓二者。不觉日日凑合。无间于吾方寸之中。是岂非事半而功倍者乎。又有一事尾及焉。凡致膰之礼。有大小通行之例。今自德院。只令一院隶负而至。贱陋初不足以当此任。而既重违吾党之望。冒没带长贰之名。则其礼似不当若是。非礼而受。岂止自损而已。重地体貌。从此坠落。此深可恨。敢将还付。悚叹悚叹。教诏士林。俾达愚见。幸甚幸甚。
拟安排。只从面前见在之处。随分整顿。随分讲究。待其积累将去。意味渐长。虽欲暂辍。有不可得焉。何可于未始发轫而先虑其害之者耶。高明自少所诵习。无非圣贤书。虽谓博览多识。何以过之。只其所主者。在彼不在此。故书与我未免为二。今若一转其几。前所谓二者。不觉日日凑合。无间于吾方寸之中。是岂非事半而功倍者乎。又有一事尾及焉。凡致膰之礼。有大小通行之例。今自德院。只令一院隶负而至。贱陋初不足以当此任。而既重违吾党之望。冒没带长贰之名。则其礼似不当若是。非礼而受。岂止自损而已。重地体貌。从此坠落。此深可恨。敢将还付。悚叹悚叹。教诏士林。俾达愚见。幸甚幸甚。答河应瑞
换节三而声息杳然。同人之怀。若追逝深。即于院人便。远辱书教。有如衡席而谈。不觉巴东之接煦认也。闾梗快霁。斋中玩赏。逢秋尤佳。益为喜泻区区。第惟缕缕所教。犹不能无疑。槩从前追愆之意。叹逝之恨。固是好消息。然苟不安于自▼(日/出/恭)弃者。孰无此心。而若不特地竖起劄住。猛勇担著。不觉若存若亡。而无以自立。而与不知悔者。同归宿者。乃高才美质之所不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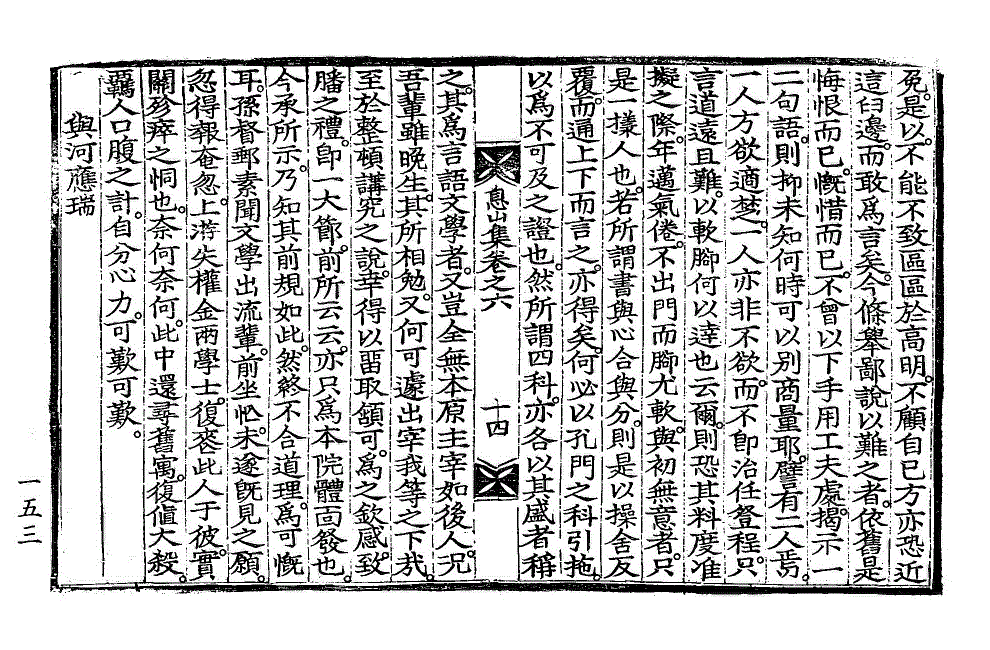 免。是以。不能不致区区于高明。不顾自己方亦恐近这臼边。而敢为言矣。今条举鄙说以难之者。依旧是悔恨而已。慨惜而已。不曾以下手用工夫处。揭示一二句语。则抑未知何时可以别商量耶。譬有二人焉。一人方欲适楚。一人亦非不欲。而不即治任登程。只言道远且难。以软脚何以达也云尔。则恐其料度准拟之际。年迈气倦。不出门而脚尤软。与初无意者。只是一㨾人也。若所谓书与心合与分。则是以操舍反覆。而通上下而言之。亦得矣。何必以孔门之科引拖。以为不可及之證也。然所谓四科。亦各以其盛者称之。其为言语文学者。又岂全无本原主宰如后人。况吾辈虽晚生。其所相勉。又何可遽出宰我等之下哉。至于整顿讲究之说。幸得以留取颔可。为之钦感。致膰之礼。即一大节。前所云云。亦只为本院体面发也。今承所示。乃知其前规如此。然终不合道理。为可慨耳。孙督邮素闻文学出流辈。前坐忙。未遂既见之愿。忽得报奄忽。上游失权金两学士。复丧此人于彼。实关殄瘁之恫也。奈何奈何。此中还寻旧寓。复值大杀。羁人口腹之计。自分心力。可叹可叹。
免。是以。不能不致区区于高明。不顾自己方亦恐近这臼边。而敢为言矣。今条举鄙说以难之者。依旧是悔恨而已。慨惜而已。不曾以下手用工夫处。揭示一二句语。则抑未知何时可以别商量耶。譬有二人焉。一人方欲适楚。一人亦非不欲。而不即治任登程。只言道远且难。以软脚何以达也云尔。则恐其料度准拟之际。年迈气倦。不出门而脚尤软。与初无意者。只是一㨾人也。若所谓书与心合与分。则是以操舍反覆。而通上下而言之。亦得矣。何必以孔门之科引拖。以为不可及之證也。然所谓四科。亦各以其盛者称之。其为言语文学者。又岂全无本原主宰如后人。况吾辈虽晚生。其所相勉。又何可遽出宰我等之下哉。至于整顿讲究之说。幸得以留取颔可。为之钦感。致膰之礼。即一大节。前所云云。亦只为本院体面发也。今承所示。乃知其前规如此。然终不合道理。为可慨耳。孙督邮素闻文学出流辈。前坐忙。未遂既见之愿。忽得报奄忽。上游失权金两学士。复丧此人于彼。实关殄瘁之恫也。奈何奈何。此中还寻旧寓。复值大杀。羁人口腹之计。自分心力。可叹可叹。与河应瑞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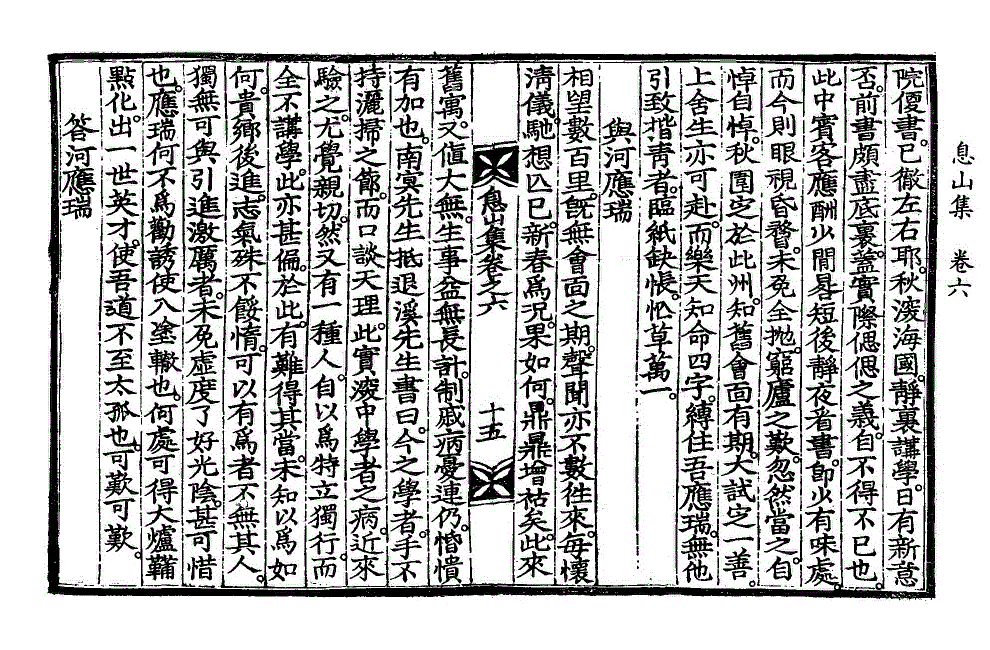 院便书。已彻左右耶。秋深海国。静里讲学。日有新意否。前书颇尽底里。盖实际偲偲之义。自不得不已也。此中宾客应酬少閒晷短后静夜看书。即少有味处。而今则眼视昏瞀。未免全抛。穷庐之叹。忽然当之。自悼自悼。秋围定于此州。知旧会面有期。大试定一善。上舍生亦可赴。而乐天知命四字。縳住吾应瑞。无他引致揩青者。临纸缺怅。忙草万一。
院便书。已彻左右耶。秋深海国。静里讲学。日有新意否。前书颇尽底里。盖实际偲偲之义。自不得不已也。此中宾客应酬少閒晷短后静夜看书。即少有味处。而今则眼视昏瞀。未免全抛。穷庐之叹。忽然当之。自悼自悼。秋围定于此州。知旧会面有期。大试定一善。上舍生亦可赴。而乐天知命四字。縳住吾应瑞。无他引致揩青者。临纸缺怅。忙草万一。与河应瑞
相望数百里。既无会面之期。声闻亦不数往来。每怀清仪。驰想亡已。新春为况。果如何。鼎鼎增祜矣。此来旧寓。又值大无。生事益无长计。制戚病忧连仍。惛愦有加也。南冥先生抵退溪先生书曰。今之学者。手不持洒扫之节。而口谈天理。此实深中学者之病。近来验之。尤觉亲切。然又有一种人。自以为特立独行。而全不讲学。此亦甚偏。于此。有难得其当。未知以为如何。贵乡后进。志气殊不馁惰。可以有为者不无其人。独无可与引进激厉者。未免虚度了好光阴。甚可惜也。应瑞何不为劝诱使入涂辙也。何处可得大炉鞴点化。出一世英才。使吾道不至太孤也。可叹可叹。
答河应瑞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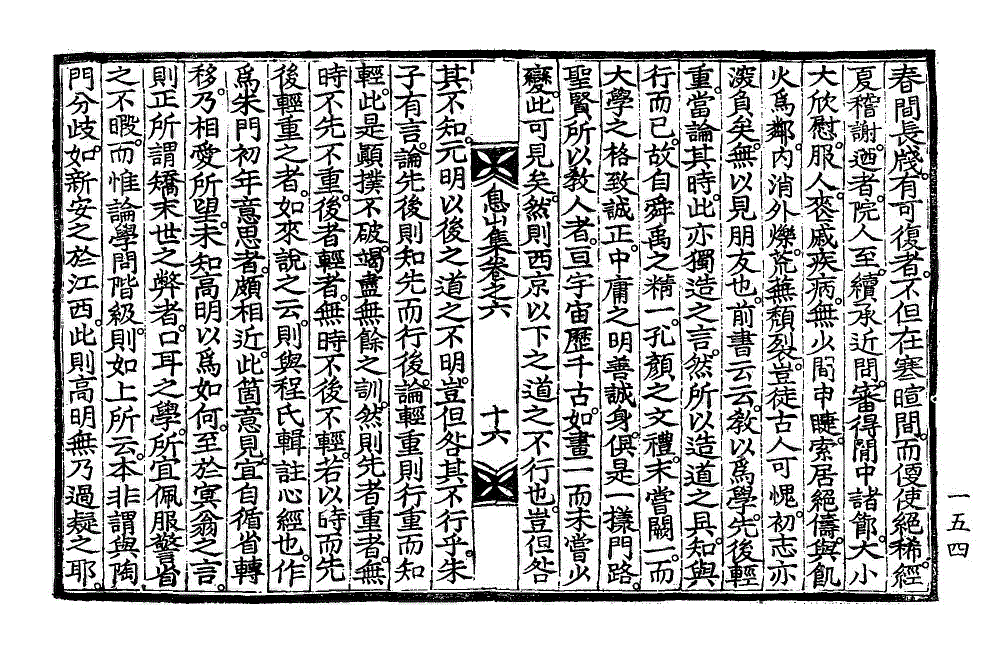 春间长笺。有可复者。不但在寒暄间。而便使绝稀。经夏稽谢。乃者。院人至。续承近问。审得閒中诸节。大小大欣慰。服人。丧戚疾病。无少间申睫。索居绝俦。与饥火为邻。内消外烁。荒芜颓裂。岂徒古人可愧。初志亦深负矣。无以见朋友也。前书云云。教以为学。先后轻重。当论其时。此亦独造之言。然所以造道之具。知与行而已。故自舜禹之精一。孔颜之文礼。未尝阙一。而大学之格致诚正。中庸之明善诚身。俱是一㨾门路。圣贤所以教人者。亘宇宙历千古。如画一而未尝少变。此可见矣。然则西京以下之道之不行也。岂但咎其不知。元明以后之道之不明。岂但咎其不行乎。朱子有言。论先后则知先而行后。论轻重则行重而知轻。此是颠扑不破。竭尽无馀之训。然则先者重者。无时不先不重。后者轻者。无时不后不轻。若以时而先后轻重之者。如来说之云。则与程氏辑注心经也。作为朱门初年意思者。颇相近。此个意见。宜自循省转移。乃相爱所望。未知高明以为如何。至于冥翁之言。则正所谓矫末世之弊者。口耳之学。所宜佩服警省之不暇。而惟论学问阶级。则如上所云。本非谓与陶门分歧。如新安之于江西。此则高明无乃过疑之耶。
春间长笺。有可复者。不但在寒暄间。而便使绝稀。经夏稽谢。乃者。院人至。续承近问。审得閒中诸节。大小大欣慰。服人。丧戚疾病。无少间申睫。索居绝俦。与饥火为邻。内消外烁。荒芜颓裂。岂徒古人可愧。初志亦深负矣。无以见朋友也。前书云云。教以为学。先后轻重。当论其时。此亦独造之言。然所以造道之具。知与行而已。故自舜禹之精一。孔颜之文礼。未尝阙一。而大学之格致诚正。中庸之明善诚身。俱是一㨾门路。圣贤所以教人者。亘宇宙历千古。如画一而未尝少变。此可见矣。然则西京以下之道之不行也。岂但咎其不知。元明以后之道之不明。岂但咎其不行乎。朱子有言。论先后则知先而行后。论轻重则行重而知轻。此是颠扑不破。竭尽无馀之训。然则先者重者。无时不先不重。后者轻者。无时不后不轻。若以时而先后轻重之者。如来说之云。则与程氏辑注心经也。作为朱门初年意思者。颇相近。此个意见。宜自循省转移。乃相爱所望。未知高明以为如何。至于冥翁之言。则正所谓矫末世之弊者。口耳之学。所宜佩服警省之不暇。而惟论学问阶级。则如上所云。本非谓与陶门分歧。如新安之于江西。此则高明无乃过疑之耶。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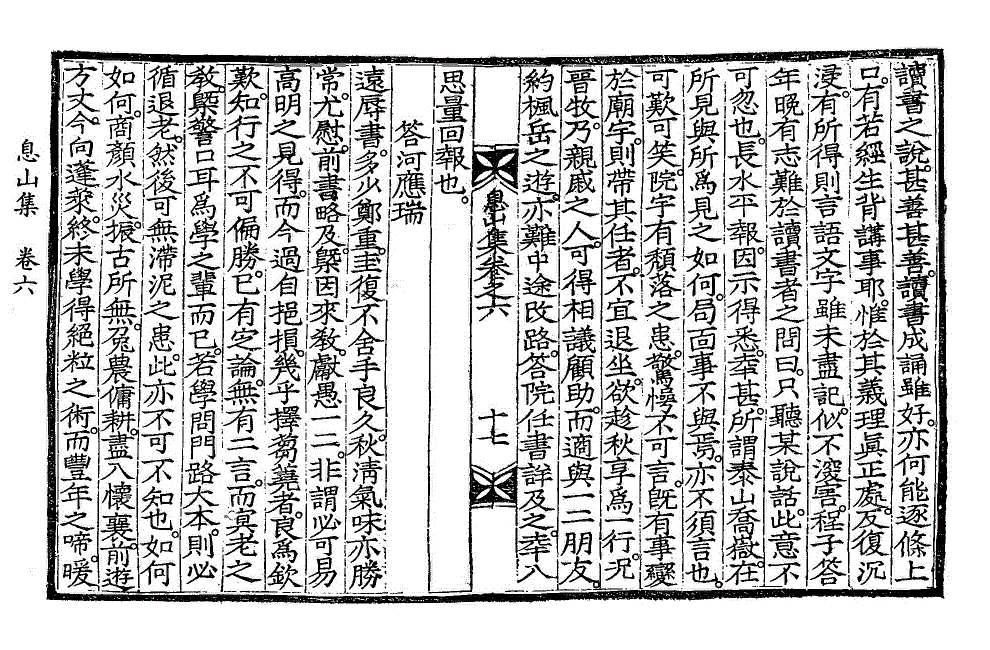 读书之说。甚善甚善。读书成诵虽好。亦何能逐条上口。有若经生背讲事耶。惟于其义理真正处。反复沉浸。有所得则言语文字虽未尽记。似不深害。程子答年晚有志难于读书者之问曰。只听某说话。此意不可忽也。长水平报。因示得悉。幸甚。所谓泰山乔岳。在所见与所为见之如何。局面事不与焉。亦不须言也。可叹可笑。院宇有颓落之患。惊愕不可言。既有事变于庙宇。则带其任者。不宜退坐。欲趁秋享为一行。况晋牧。乃亲戚之人。可得相议顾助。而适与一二朋友。约枫岳之游。亦难中途改路。答院任书详及之。幸入思量回报也。
读书之说。甚善甚善。读书成诵虽好。亦何能逐条上口。有若经生背讲事耶。惟于其义理真正处。反复沉浸。有所得则言语文字虽未尽记。似不深害。程子答年晚有志难于读书者之问曰。只听某说话。此意不可忽也。长水平报。因示得悉。幸甚。所谓泰山乔岳。在所见与所为见之如何。局面事不与焉。亦不须言也。可叹可笑。院宇有颓落之患。惊愕不可言。既有事变于庙宇。则带其任者。不宜退坐。欲趁秋享为一行。况晋牧。乃亲戚之人。可得相议顾助。而适与一二朋友。约枫岳之游。亦难中途改路。答院任书详及之。幸入思量回报也。答河应瑞
远辱书。多少郑重。圭复不舍手良久。秋清气味亦胜常。尤慰。前书略及。槩因来教。献愚一二。非谓必可易高明之见得。而今过自挹损。几乎择刍荛者。良为钦叹。知行之不可偏胜。已有定论。无有二言。而冥老之教。槩警口耳为学之辈而已。若学问门路大本。则必循退老。然后可无滞泥之患。此亦不可不知也。如何如何。商颜水灾。振古所无。兔农佣耕。尽入怀襄。前游方丈。今向蓬莱。终未学得绝粒之术。而丰年之啼。暖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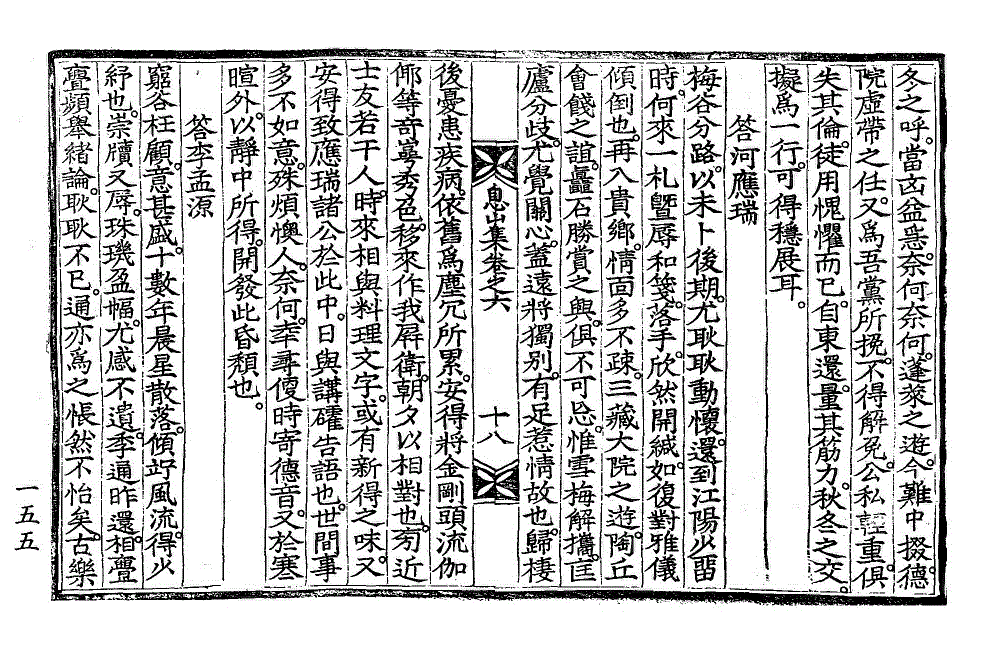 冬之呼。当凶益急。奈何奈何。蓬莱之游。今难中掇。德院虚带之任。又为吾党所挽。不得解免。公私轻重。俱失其伦。徒用愧惧而已。自东还。量其筋力。秋冬之交。拟为一行。可得稳展耳。
冬之呼。当凶益急。奈何奈何。蓬莱之游。今难中掇。德院虚带之任。又为吾党所挽。不得解免。公私轻重。俱失其伦。徒用愧惧而已。自东还。量其筋力。秋冬之交。拟为一行。可得稳展耳。答河应瑞
梅谷分路。以未卜后期。尤耿耿动怀。还到江阳少留时。何来一札暨辱和笺。落手。欣然开缄。如复对雅仪倾倒也。再入贵乡。情面多不疏。三藏大院之游。陶丘会饯之谊。矗石胜赏之兴。俱不可忘。惟雪梅解携。匡庐分歧。尤觉关心。盖远将独别。有足惹情故也。归栖后忧患疾病。依旧为尘冗所累。安得将金刚头流伽倻等奇崿秀色。移来作我屏卫。朝夕以相对也。旁近士友若干人。时来相与料理文字。或有新得之味。又安得致应瑞诸公于此中。日与讲礭告语也。世间事多不如意。殊烦懊人。奈何。幸寻便时寄德音。又于寒暄外。以静中所得。开发此昏颓也。
答李孟源
穷谷枉顾。意甚盛。十数年晨星散落。倾伫风流。得少纾也。崇牍又辱。珠玑盈幅。尤感不遗。季通昨还。相亹亹频举绪论。耿耿不已。通亦为之怅然不怡矣。古乐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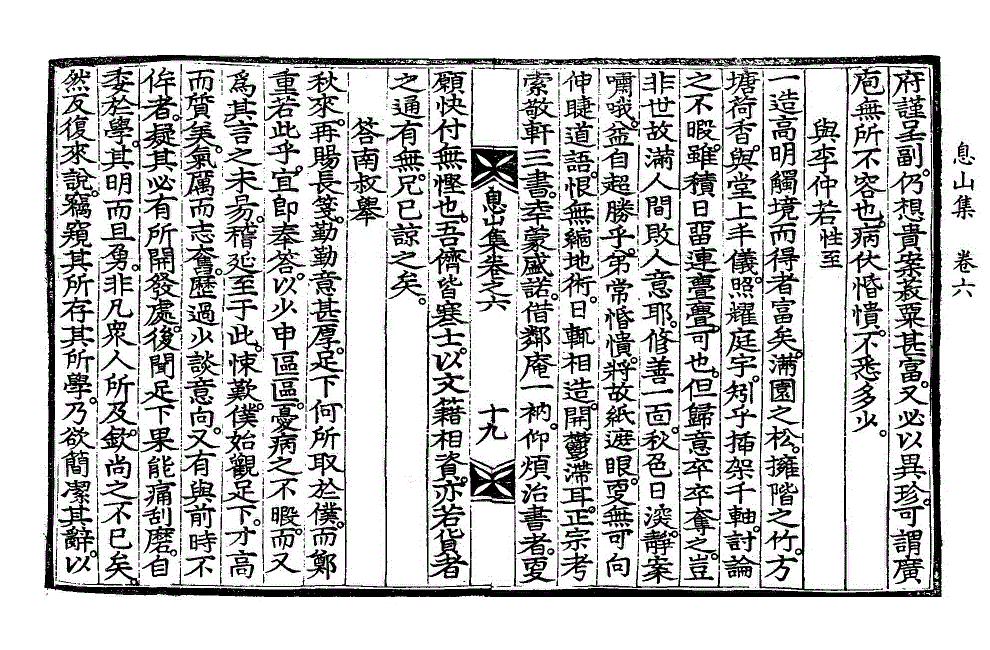 府谨呈副。仍想贵案菽粟甚富。又必以异珍。可谓广庖无所不容也。病伏惛愦。不悉多少。
府谨呈副。仍想贵案菽粟甚富。又必以异珍。可谓广庖无所不容也。病伏惛愦。不悉多少。与李仲若(性至)
一造高明触境而得者富矣。满园之松。拥阶之竹。方塘荷香。与堂上丰仪。照耀庭宇。矧乎插架千轴。讨论之不暇。虽积日留连亹亹。可也。但归意卒卒夺之。岂非世故满人间败人意耶。修善一面。秋色日深。静案啸哦。益自超胜乎。弟常惛愦。将故纸遮眼。更无可向伸睫道语。恨无缩地术。日辄相造。开郁滞耳。正宗考索敬轩三书。幸蒙盛诺。借邻庵一衲。仰烦治书者。更愿快付无悭也。吾侪皆寒士。以文籍相资。亦若货者之通有无。兄已谅之矣。
答南叔举
秋来。再赐长笺。勤勤意甚厚。足下何所取于仆。而郑重若此乎。宜即奉答。以少申区区。忧病之不暇。而又为其言之未易。稽延至于此。悚叹。仆始观足下。才高而质美。气厉而志奋。历过少谈意向。又有与前时不侔者。疑其必有所开发处。后闻足下果能痛刮磨。自委于学。其明而且勇。非凡众人所及。钦尚之不已矣。然反复来说。窃窥其所存其所学。乃欲简洁其辞。以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6L 页
 追古作者则度。则此非仆之所及也。仆之所愿与朋友讲之者。在于道。道在日用彝伦之间。人所当为当行者。是也。仆鲁下。又未力行于道。无所窥畔。以是为忧。苟有得于道。其发之以为文者。自不患不及夫古人。何必规规然捐时弊精。学为如是之文乎。人事之学未至。徒以记诵辞章。誇多而偷靡。君子不贵也。虽然。道之寓于言而传于后。非文不能。故学者。亦不可不读书。读书果为文辞耶。抑为道耶。大抵诗。明三纲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书。记先王德行,政事,命令,诰诫。礼。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别嫌疑。严等威。正人纪。乐。谐神人。和上下。协万邦。春秋。大一统。定民志。褒善纠恶。易。言万化之变。察于几微。存戒惧。守正虑患。鲁论及邹书。记圣贤言行。曾思之传。述道学大经大法。以明道统。故诗长于风。书长于政。礼长于别。乐长于和。春秋长于权。易长于变化。循习服行。莫过于四传。此六经之教。圣贤之书。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然则读书。舍是亦何所用哉。仆少也。妄意不自揆。欲古人之追及。虽略知以圣贤为准则。而为己之意不实。不知用力缓急。务博好新之心胜。是以渐自放纵浸淫。六经四传之外。如老氏之言道德。列御寇,庄周之
追古作者则度。则此非仆之所及也。仆之所愿与朋友讲之者。在于道。道在日用彝伦之间。人所当为当行者。是也。仆鲁下。又未力行于道。无所窥畔。以是为忧。苟有得于道。其发之以为文者。自不患不及夫古人。何必规规然捐时弊精。学为如是之文乎。人事之学未至。徒以记诵辞章。誇多而偷靡。君子不贵也。虽然。道之寓于言而传于后。非文不能。故学者。亦不可不读书。读书果为文辞耶。抑为道耶。大抵诗。明三纲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书。记先王德行,政事,命令,诰诫。礼。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别嫌疑。严等威。正人纪。乐。谐神人。和上下。协万邦。春秋。大一统。定民志。褒善纠恶。易。言万化之变。察于几微。存戒惧。守正虑患。鲁论及邹书。记圣贤言行。曾思之传。述道学大经大法。以明道统。故诗长于风。书长于政。礼长于别。乐长于和。春秋长于权。易长于变化。循习服行。莫过于四传。此六经之教。圣贤之书。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然则读书。舍是亦何所用哉。仆少也。妄意不自揆。欲古人之追及。虽略知以圣贤为准则。而为己之意不实。不知用力缓急。务博好新之心胜。是以渐自放纵浸淫。六经四传之外。如老氏之言道德。列御寇,庄周之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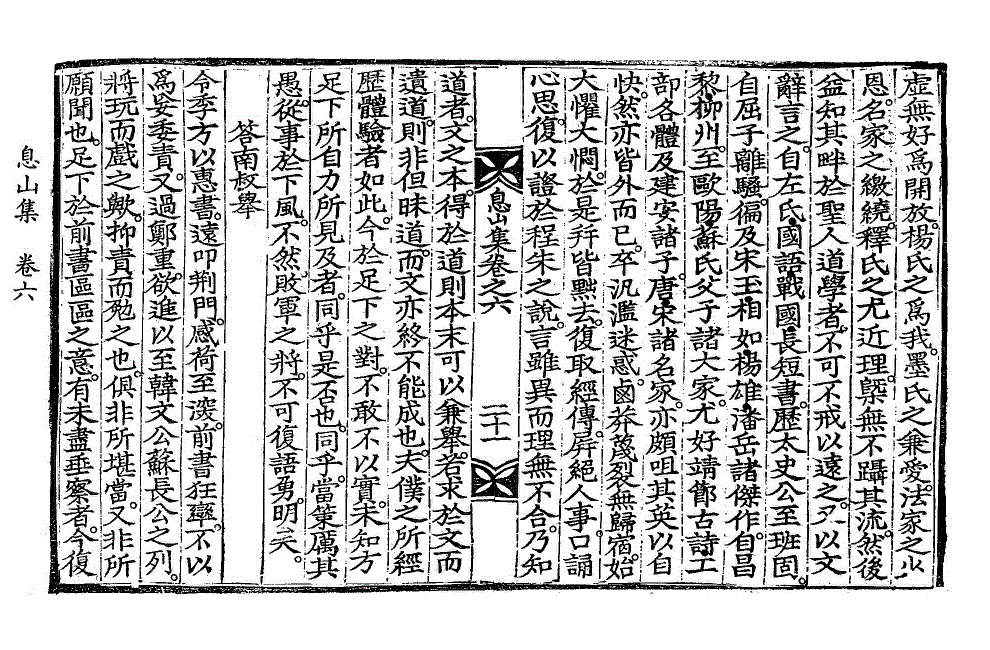 虚无好为开放。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法家之少恩。名家之缴绕。释氏之尤近理。槩无不蹑其流。然后益知其畔于圣人道学者。不可不戒以远之。又以文辞言之。自左氏,国语,战国,长短书。历太史公至班固。自屈子离骚。遍及宋玉,相如,杨雄,潘岳诸杰作。自昌黎,柳州。至欧阳,苏氏父子诸大家。尤好靖节古诗,工部各体及建安诸子。唐,宋诸名家。亦颇咀其英以自快。然亦皆外而已。卒汎滥迷惑。卤莽蔑裂无归宿。始大惧大悯。于是并皆黜去。复取经传。屏绝人事。口诵心思。复以證于程朱之说。言虽异而理无不合。乃知道者。文之本。得于道则本末可以兼举。若求于文而遗道。则非但昧道。而文亦终不能成也。夫仆之所经历体验者如此。今于足下之对。不敢不以实。未知方足下所自力所见及者。同乎是否也。同乎。当策厉其愚。从事于下风。不然。败军之将。不可复语勇。明矣。
虚无好为开放。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法家之少恩。名家之缴绕。释氏之尤近理。槩无不蹑其流。然后益知其畔于圣人道学者。不可不戒以远之。又以文辞言之。自左氏,国语,战国,长短书。历太史公至班固。自屈子离骚。遍及宋玉,相如,杨雄,潘岳诸杰作。自昌黎,柳州。至欧阳,苏氏父子诸大家。尤好靖节古诗,工部各体及建安诸子。唐,宋诸名家。亦颇咀其英以自快。然亦皆外而已。卒汎滥迷惑。卤莽蔑裂无归宿。始大惧大悯。于是并皆黜去。复取经传。屏绝人事。口诵心思。复以證于程朱之说。言虽异而理无不合。乃知道者。文之本。得于道则本末可以兼举。若求于文而遗道。则非但昧道。而文亦终不能成也。夫仆之所经历体验者如此。今于足下之对。不敢不以实。未知方足下所自力所见及者。同乎是否也。同乎。当策厉其愚。从事于下风。不然。败军之将。不可复语勇。明矣。答南叔举
令季方以惠书。远叩荆门。感荷至深。前书狂率。不以为妄委责。又过郑重。欲进以至韩文公苏长公之列。将玩而戏之欤。抑责而勉之也。俱非所堪当。又非所愿闻也。足下于前书区区之意。有未尽垂察者。今复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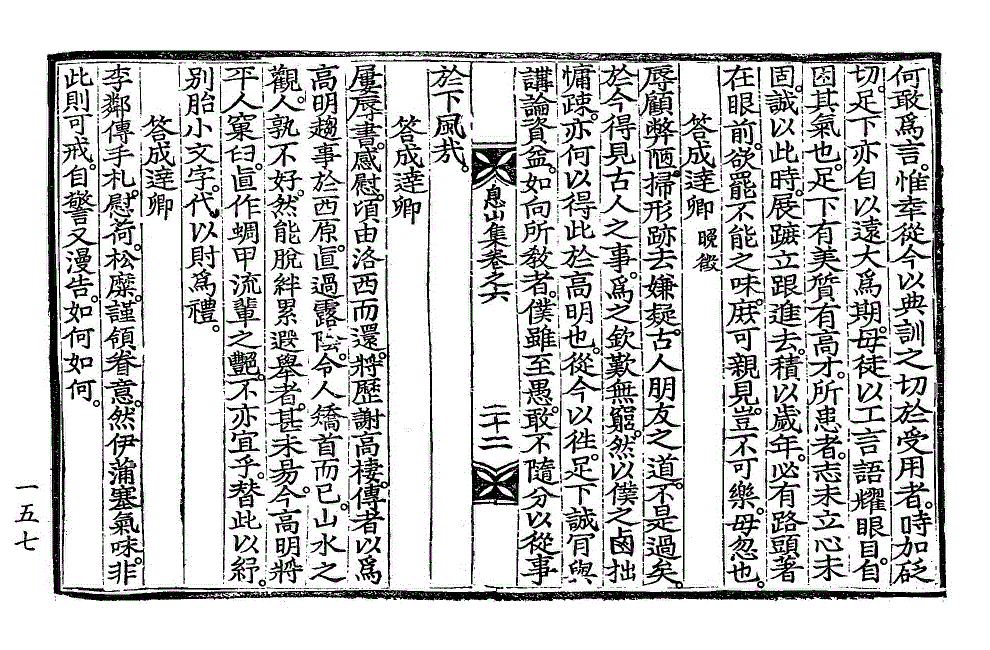 何敢为言。惟幸从今以典训之切于受用者。时加砭切。足下亦自以远大为期。毋徒以工言语耀眼目。自困其气也。足下有美质有高才。所患者。志未立心未固。诚以此时。展蹠立跟进去。积以岁年。必有路头著在眼前。欲罢不能之味。庶可亲见。岂不可乐。毋忽也。
何敢为言。惟幸从今以典训之切于受用者。时加砭切。足下亦自以远大为期。毋徒以工言语耀眼目。自困其气也。足下有美质有高才。所患者。志未立心未固。诚以此时。展蹠立跟进去。积以岁年。必有路头著在眼前。欲罢不能之味。庶可亲见。岂不可乐。毋忽也。答成达卿(晚徵)
辱顾弊陋。扫形迹去嫌疑。古人朋友之道。不是过矣。于今得见古人之事。为之钦叹无穷。然以仆之卤拙慵疏。亦何以得此于高明也。从今以往。足下诚肯与讲论资益。如向所教者。仆虽至愚。敢不随分以从事于下风哉。
答成达卿
屡辱书。感慰。顷由洛西而还。将历谢高栖。传者以为高明趋事于西原。直过露阴。令人矫首而已。山水之观。人孰不好。然能脱绊累遐举者。甚未易。今高明将平人窠臼。直作蜩甲流辈之艳。不亦宜乎。替此以纾。别胎小文字。代以财为礼。
答成达卿
李邻传手札。慰荷。松糜。谨领眷意。然伊蒲塞气味。非此则可戒。自警又漫告。如何如何。
答成达卿
惠帖良慰。仆归栖。日恼旱炎。山中馀趣。可知消歇无馀。分华之示。亦令人起立。然仆每自比堀土蚓虫以无他事。惟以兔农勤力为务故也。高明已作田龙。欲与蚓虫。分据洞壑拟议。恐皆失伦。且闻龙游洞上。有新搆。其中则亦有田龙。高明可谋同飞。何足顾蚓虫耶。可笑可笑。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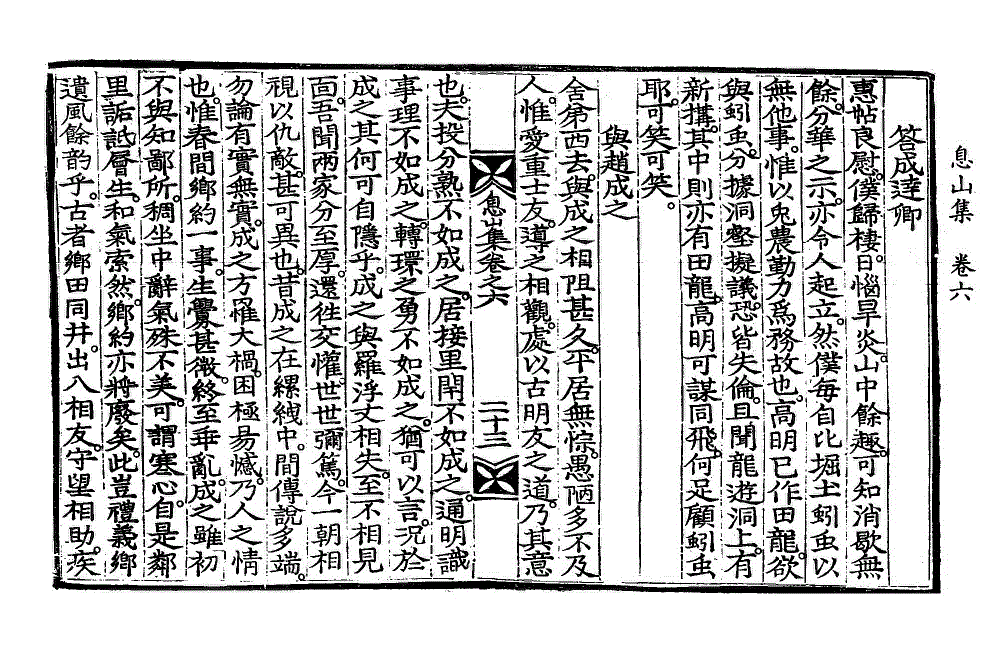 与赵成之
与赵成之舍弟西去。与成之相阻甚久。平居无悰。愚陋多不及人。惟爱重士友。导之相观。处以古朋友之道。乃其意也。夫投分熟不如成之。居接里闬不如成之。通明识事理不如成之。转环之勇不如成之。犹可以言。况于成之其何可自隐乎。成之与罗浮丈相失。至不相见面。吾闻两家分至厚。还往交欢。世世弥笃。今一朝相视以仇敌。甚可异也。昔成之在缧绁中。间传说多端。勿论有实无实。成之方罹大祸。困极易憾。乃人之情也。惟春间乡约一事。生衅甚微。终至乖乱。成之虽初不与知鄙所。稠坐中辞气殊不美。可谓寒心。自是邻里诟诋层生。和气索然。乡约亦将废矣。此岂礼义乡遗风馀韵乎。古者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8L 页
 病相扶持。三代劝民善俗。以此为大。后世乡约之法。乃其遗制也。故邻里有兄弟之义。更与之同约。累世从事。疾病死丧忧喜庆戚。莫不相仗。岂宜因一愤懥。各存其私。惟务强戾。少不相逊。使美俗良规。亦任其残灭乎。先辈刱之甚勤。后人坏之甚▼(日/出/恭)。先辈为睦邻里厚来往而设之。后人与邻里争鬨而罢之。又何先后之用心太相反也。虽然。春秋之义。责贤者备。是以。独于我成之。不顾闭门之戒。先进眷眷。敢陈瞽说。未知成之以为如何。大抵洞人保合。乡约修复。只在成之反复间。成之亦知之耶。前事是非。他人得失。置勿论。驳通作于贤季。诋言发于尊口。罗浮之引退。不欲同事。出于不得已也。退之以不得已。而进之以可已。虽偶人亦不肯。况罗浮乎。故成之必先改图。然后罗浮之怒可解。洞人之疑可破。乡约之废可复。成之其可不念焉。凡为成之谋者。或必曰。彼丈夫我丈夫也。吾何先屈。是适误成之。非谋之之忠者。流俗之人。以盛气力胜为快。以虚己受人为耻。乃偏滞恨愎之事。岂以成之读古人书。不自菲薄而循其辙也。昔蔺相如战国之侠士。能自退逊。使廉颇负荆请罪。今成之苟如相如之所为。则罗浮虽未出廉颇之计。曲直当
病相扶持。三代劝民善俗。以此为大。后世乡约之法。乃其遗制也。故邻里有兄弟之义。更与之同约。累世从事。疾病死丧忧喜庆戚。莫不相仗。岂宜因一愤懥。各存其私。惟务强戾。少不相逊。使美俗良规。亦任其残灭乎。先辈刱之甚勤。后人坏之甚▼(日/出/恭)。先辈为睦邻里厚来往而设之。后人与邻里争鬨而罢之。又何先后之用心太相反也。虽然。春秋之义。责贤者备。是以。独于我成之。不顾闭门之戒。先进眷眷。敢陈瞽说。未知成之以为如何。大抵洞人保合。乡约修复。只在成之反复间。成之亦知之耶。前事是非。他人得失。置勿论。驳通作于贤季。诋言发于尊口。罗浮之引退。不欲同事。出于不得已也。退之以不得已。而进之以可已。虽偶人亦不肯。况罗浮乎。故成之必先改图。然后罗浮之怒可解。洞人之疑可破。乡约之废可复。成之其可不念焉。凡为成之谋者。或必曰。彼丈夫我丈夫也。吾何先屈。是适误成之。非谋之之忠者。流俗之人。以盛气力胜为快。以虚己受人为耻。乃偏滞恨愎之事。岂以成之读古人书。不自菲薄而循其辙也。昔蔺相如战国之侠士。能自退逊。使廉颇负荆请罪。今成之苟如相如之所为。则罗浮虽未出廉颇之计。曲直当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9H 页
 自分矣。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孰不仰高明而归美乎。惟成之勉之。若肯采听愚言。请卜閒暇之日。幽旷之所。咸集少长。肴酒相属。一言以破胶固之私。数酌以畅谐和之气。竟夕尽欢。如寇贾之事。使群疑众嫌。一时冰释。既渝之俗。渐可敦矣。既失之和。渐可复矣。既罢之乡约。渐可修举矣。岂不幸甚。成之气清识透。第有太阳馀症。幸平心易气。公听并观。勿以人废言也。
自分矣。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孰不仰高明而归美乎。惟成之勉之。若肯采听愚言。请卜閒暇之日。幽旷之所。咸集少长。肴酒相属。一言以破胶固之私。数酌以畅谐和之气。竟夕尽欢。如寇贾之事。使群疑众嫌。一时冰释。既渝之俗。渐可敦矣。既失之和。渐可复矣。既罢之乡约。渐可修举矣。岂不幸甚。成之气清识透。第有太阳馀症。幸平心易气。公听并观。勿以人废言也。答赵成之
辱惠书。迨一月稽报。深愧不敏。来书甚博。纵横出没。令人有未领其体要者。閒中所得。亦不少矣。盖卜筑之全。江山之美。本非不足。更得真宰变化。昔野之地。今益幽旷。昔无之泉。今忽涌出。岩铲其顽而壑改其姿。而高明之赏。亦昔皮而今里。命名岩台。极其美盛。感天人之际。显晦之有时。而仁智之乐。至于手舞而足蹈。天之饷吾人。可谓不偶然矣。然所可怪者。既以为乐之深。而反以存之之妙。养之之妙。问于人何也。由前之说。则先乐而后存之养之。非愚之所闻也。由后说。则高明之所谓乐者。恐只在影想之间也。何者。窃为反覆来教。究其旨意所在。则不过以好江山。詑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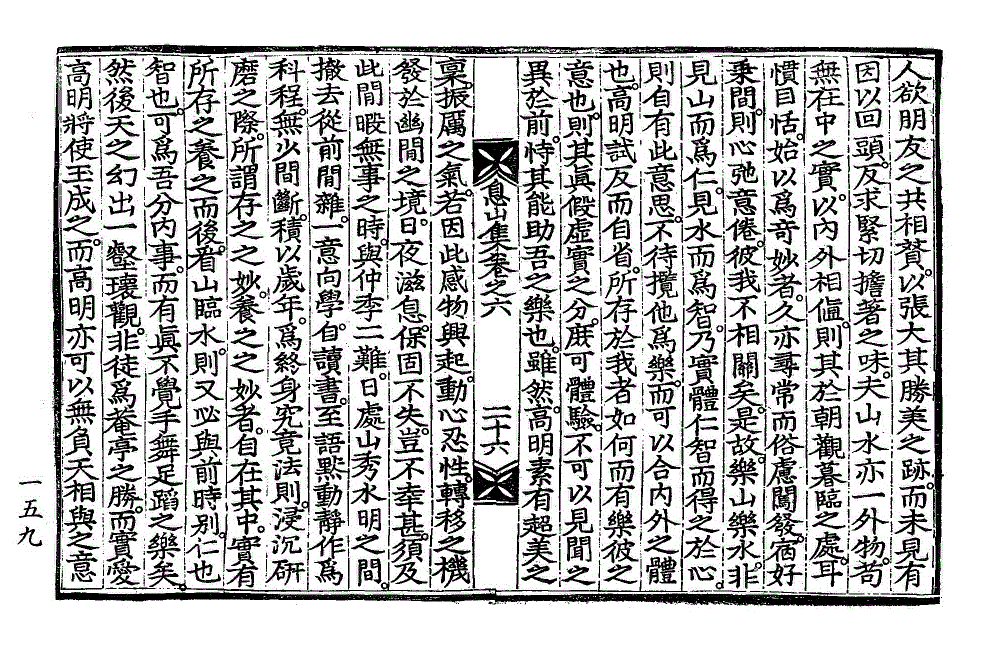 人欲朋友之共相赞。以张大其胜美之迹。而未见有因以回头。反求紧切担著之味。夫山水亦一外物。苟无在中之实。以内外相值。则其于朝观暮临之处。耳惯目恬。始以为奇妙者。久亦寻常而俗虑闯发。宿好乘间。则心弛意倦。彼我不相关矣。是故。乐山乐水。非见山而为仁。见水而为智。乃实体仁智而得之于心。则自有此意思。不待揽他为乐。而可以合内外之体也。高明试反而自省。所存于我者如何而有乐彼之意也。则其真假虚实之分。庶可体验。不可以见闻之异于前。恃其能助吾之乐也。虽然。高明素有超美之禀。振厉之气。若因此感物兴起。动心忍性。转移之机发于幽閒之境。日夜滋息。保固不失。岂不幸甚。须及此閒暇无事之时。与仲季二难。日处山秀水明之间。撤去从前閒杂。一意向学。自读书。至语默动静作为科程。无少间断。积以岁年。为终身究竟法则。浸沉研磨之际。所谓存之之妙。养之之妙者。自在其中。实有所存之养之而后。看山临水。则又必与前时别。仁也智也。可为吾分内事。而有真不觉手舞足蹈之乐矣。然后天之幻出一壑瑰观。非徒为庵亭之胜。而实爱高明将使玉成之。而高明亦可以无负天相与之意
人欲朋友之共相赞。以张大其胜美之迹。而未见有因以回头。反求紧切担著之味。夫山水亦一外物。苟无在中之实。以内外相值。则其于朝观暮临之处。耳惯目恬。始以为奇妙者。久亦寻常而俗虑闯发。宿好乘间。则心弛意倦。彼我不相关矣。是故。乐山乐水。非见山而为仁。见水而为智。乃实体仁智而得之于心。则自有此意思。不待揽他为乐。而可以合内外之体也。高明试反而自省。所存于我者如何而有乐彼之意也。则其真假虚实之分。庶可体验。不可以见闻之异于前。恃其能助吾之乐也。虽然。高明素有超美之禀。振厉之气。若因此感物兴起。动心忍性。转移之机发于幽閒之境。日夜滋息。保固不失。岂不幸甚。须及此閒暇无事之时。与仲季二难。日处山秀水明之间。撤去从前閒杂。一意向学。自读书。至语默动静作为科程。无少间断。积以岁年。为终身究竟法则。浸沉研磨之际。所谓存之之妙。养之之妙者。自在其中。实有所存之养之而后。看山临水。则又必与前时别。仁也智也。可为吾分内事。而有真不觉手舞足蹈之乐矣。然后天之幻出一壑瑰观。非徒为庵亭之胜。而实爱高明将使玉成之。而高明亦可以无负天相与之意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0H 页
 者也。苟然则号水名岩题咏刻板。有亦可无亦可。可不念哉。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换月初。与一二同志。寻白云,仙游二胜。厥石玉磨也。厥水琼液也。穹幽漏明。霞霱互端。时物争敷应接。有不暇领略。皆趣味也。及归栖。忧冗惛愦。好意思日觉消歇。必须存养省察。制情集义。庶几接续。益知善恶之几惟在吾心。山水之观自有术也。
者也。苟然则号水名岩题咏刻板。有亦可无亦可。可不念哉。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换月初。与一二同志。寻白云,仙游二胜。厥石玉磨也。厥水琼液也。穹幽漏明。霞霱互端。时物争敷应接。有不暇领略。皆趣味也。及归栖。忧冗惛愦。好意思日觉消歇。必须存养省察。制情集义。庶几接续。益知善恶之几惟在吾心。山水之观自有术也。又答问目
从父早逝。葬礼在迩。而只有三岁儿。未及干蛊。葬后题主。以孤儿书之。则祝文夙兴夜处等语。似是虚文。若以显辟书之。则既有嗣子。事涉失宜。未知何以则得当。
既有子。虽幼稚。不可以显辟题主。祝文则必有摄祀者。以摄祀之名告之。似宜耳。
从父之子尚幼。而且无期大功之亲。鄙生为堂侄之长。而门长诸父。同临下棺后。赠玄纁。以服制轻重。行之耶。以尊卑行之耶。
礼云。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以此言之。兄可自赠也。
朝祖不可废。而设殡于祠堂稍远之地。前期一日。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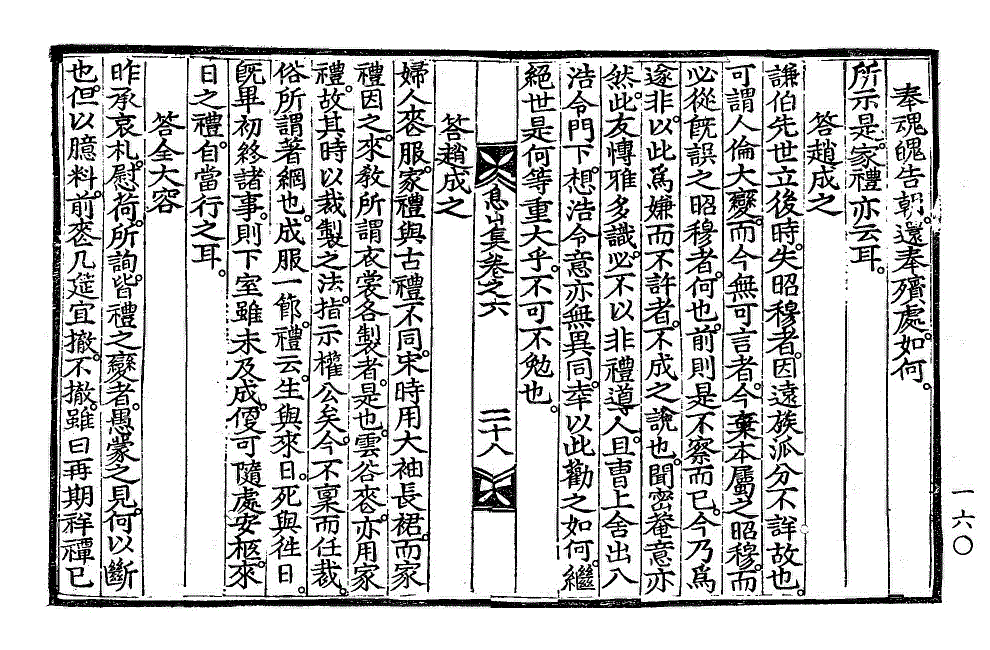 奉魂魄告朝。还奉殡处。如何。
奉魂魄告朝。还奉殡处。如何。所示是。家礼亦云耳。
答赵成之
谦伯先世立后时。失昭穆者。因远族派分不详。故也。可谓人伦大变。而今无可言者。今弃本属之昭穆。而必从既误之昭穆者。何也。前则是不察而已。今乃为遂非。以此为嫌而不许者。不成之说也。闻密庵意亦然。此友博雅多识。必不以非礼导人。且曹上舍出入浩令门下。想浩令意亦无异同。幸以此劝之如何。继绝世是何等重大乎。不可不勉也。
答赵成之
妇人丧服。家礼与古礼不同。宋时用大袖长裙。而家礼因之。来教所谓衣裳各制者。是也。云谷丧。亦用家礼。故其时以裁制之法。指示权公矣。今不禀而任裁。俗所谓著网也。成服一节。礼云。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既毕初终诸事。则下室虽未及成。便可随处安柩。来日之礼。自当行之耳。
答全大容
昨承哀札。慰荷。所询。皆礼之变者。愚蒙之见。何以断也。但以臆料。前丧几筵宜撤。不撤。虽曰再期祥禫已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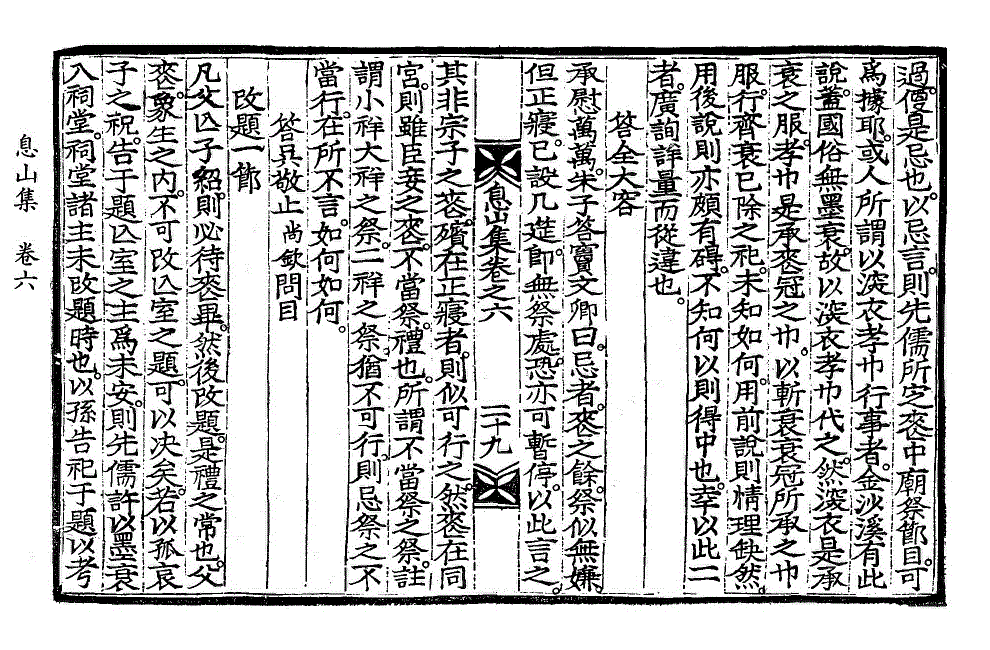 过。便是忌也。以忌言。则先儒所定丧中庙祭节目。可为据耶。或人所谓以深衣孝巾行事者。金沙溪有此说。盖国俗无墨衰。故以深衣孝巾代之。然深衣是承衰之服。孝巾是承丧冠之巾。以斩衰衰冠所承之巾服。行齐衰已除之祀。未知如何。用前说则情理缺然。用后说则亦颇有碍。不知何以则得中也。幸以此二者。广询详量而从违也。
过。便是忌也。以忌言。则先儒所定丧中庙祭节目。可为据耶。或人所谓以深衣孝巾行事者。金沙溪有此说。盖国俗无墨衰。故以深衣孝巾代之。然深衣是承衰之服。孝巾是承丧冠之巾。以斩衰衰冠所承之巾服。行齐衰已除之祀。未知如何。用前说则情理缺然。用后说则亦颇有碍。不知何以则得中也。幸以此二者。广询详量而从违也。答全大容
承慰万万。朱子答窦文卿曰。忌者。丧之馀。祭似无嫌。但正寝。已设几筵。即无祭处。恐亦可暂停。以此言之。其非宗子之丧。殡在正寝者。则似可行之。然丧在同宫。则虽臣妾之丧。不当祭。礼也。所谓不当祭之祭。注谓小祥大祥之祭。二祥之祭。犹不可行。则忌祭之不当行。在所不言。如何如何。
答吴敬止(尚钦)问目
改题一节
凡父亡子绍。则必待丧毕。然后改题。是礼之常也。父丧。象生之内。不可改亡室之题。可以决矣。若以孤哀子之祝。告于题亡室之主为未安。则先儒许以墨衰入祠堂。祠堂诸主未改题时也。以孙告祀于题以考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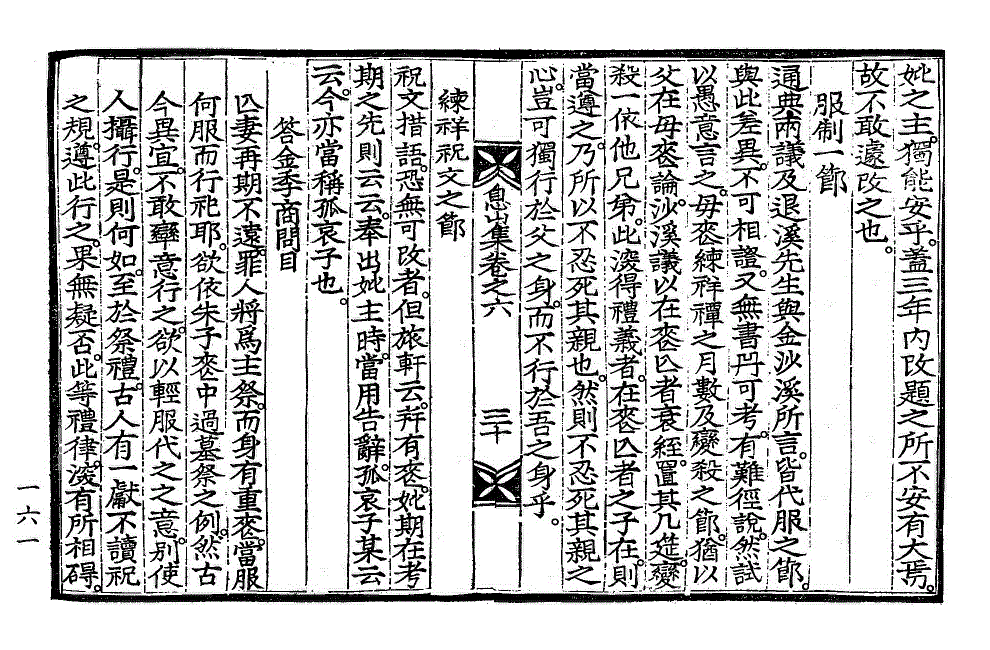 妣之主。独能安乎。盖三年内改题之所不安有大焉。故不敢遽改之也。
妣之主。独能安乎。盖三年内改题之所不安有大焉。故不敢遽改之也。服制一节
通典,两议及退溪先生与金沙溪所言。皆代服之节。与此差异。不可相證。又无书册可考。有难径说。然试以愚意言之。母丧练祥禫之月数及变杀之节。犹以父在母丧论。沙溪议以在丧亡者衰绖。置其几筵。变杀一依他兄弟。此深得礼义者。在丧亡者之子在。则当遵之。乃所以不忍死其亲也。然则不忍死其亲之心。岂可独行于父之身。而不行于吾之身乎。
练祥祝文之节
祝文措语。恐无可改者。但旅轩云。并有丧。妣期在考期之先则云云。奉出妣主时。当用告辞。孤哀子某云云。今亦当称孤哀子也。
答金季商问目
亡妻再期不远。罪人将为主祭。而身有重丧。当服何服而行祀耶。欲依朱子丧中过墓祭之例。然古今异宜。不敢率意行之。欲以轻服代之之意。别使人摄行。是则何如。至于祭礼。古人有一献不读祝之规。遵此行之。果无疑否。此等礼律。深有所相碍。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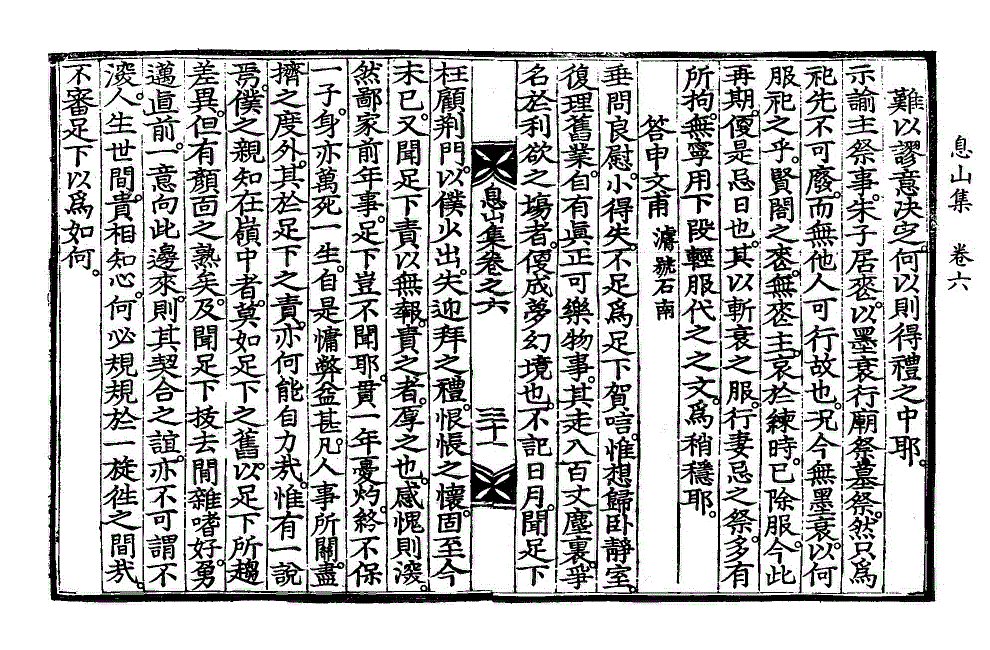 难以谬意决定。何以则得礼之中耶。
难以谬意决定。何以则得礼之中耶。示谕主祭事。朱子居丧。以墨衰行庙祭,墓祭。然只为祀先不可废。而无他人可行故也。况今无墨衰。以何服祀之乎。贤閤之丧。无丧主。哀于练时。已除服。今此再期。便是忌日也。其以斩衰之服。行妻忌之祭。多有所拘。无宁用下段轻服代之之文。为稍稳耶。
答申文甫(浚号石南)
垂问良慰。小得失。不足为足下贺唁。惟想归卧静室。复理旧业。自有真正可乐物事。其走入百丈尘里。争名于利欲之场者。便成梦幻境也。不记日月。闻足下枉顾荆门。以仆少出。失迎拜之礼。恨怅之怀。固至今未已。又闻足下责以无报。责之者。厚之也。感愧则深。然鄙家前年事。足下岂不闻耶。贯一年忧灼。终不保一子。身亦万死一生。自是慵弊益甚。凡人事所关。尽挤之度外。其于足下之责。亦何能自力哉。惟有一说焉。仆之亲知在岭中者。莫如足下之旧。以足下所趋差异。但有颜面之熟矣。及闻足下拔去閒杂嗜好。勇迈直前。一意向此边来。则其契合之谊。亦不可谓不深。人生世间。贵相知心。何必规规于一旋往之间哉。不审足下以为如何。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2L 页
 答申文甫
答申文甫前书既承悉。昨日吴致重。又送来近问。圭复久未能释矣。搬徙之苦。近来通患。最是迈厉之意。造次无替。此正好消息也。来教槩以为能看得文字。究得义理。惟于实地上无端的去处。以未有平易气象为忧。夫孰能体出近切。向人道好话。如此行之著习焉。察一言而可验。然实地工夫如何而存。平易气象如何而生。其所以资之者。恐无过读书穷理以体之身心而已也。然则高明所已能者。有未尽乎潜密精真。故无资深居安之实。而有所未能之叹乎。所宜益致其工。反身思诚。无责近效。以为至死究竟法则。似必有日计不足。月计有馀者矣。致重近与比居。必日相资益也。
答申文甫
信札连续。鄙吝不待见黄生而可消。汶上之行。令人慨然。范孟博,岑公孝事。著在简策。至今想见其风彩。其于今时非古何。为之悬仰。气象之说。谓自觉其早在。故欲以敬为主。自至于其境。理固如此。其序亦然。但入头处尤不可不审。若不以平日常行之事。为做敬之地。必归于程子所谓难久矣。何能下实地工夫。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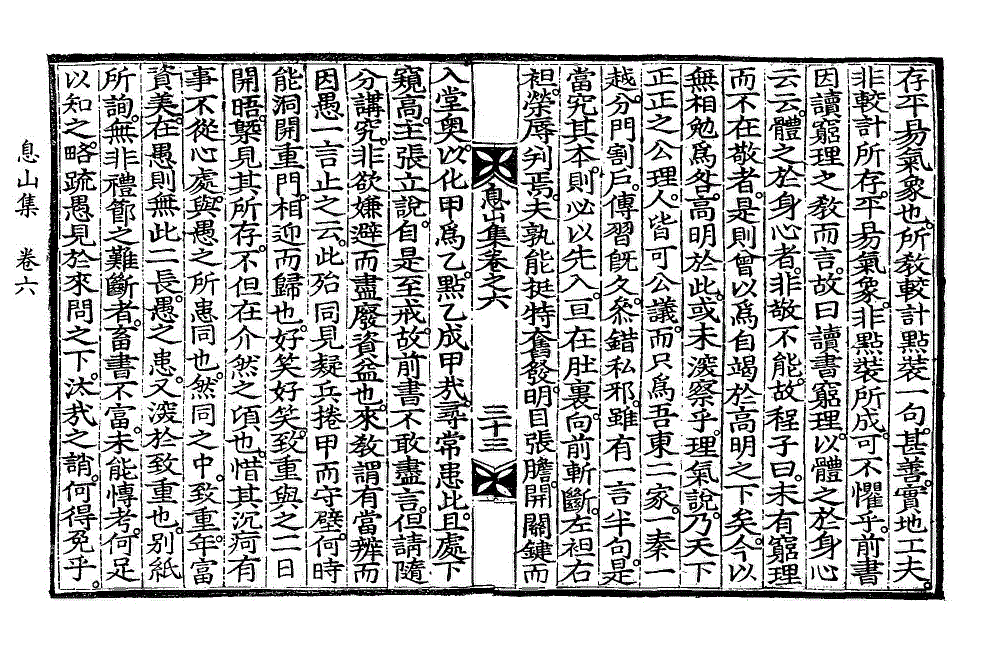 存平易气象也。所教较计点装一句。甚善。实地工夫。非较计所存。平易气象。非点装所成。可不惧乎。前书因读穷理之教而言。故曰读书穷理。以体之于身心云云。体之于身心者。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未有穷理而不在敬者。是则曾以为自竭于高明之下矣。今以无相勉为咎。高明于此。或未深察乎。理气说。乃天下正正之公理。人皆可公议。而只为吾东二家。一秦一越。分门割户。传习既久。参错私邪。虽有一言半句。是当究其本。则必以先入。亘在肚里。向前斩断。左袒右袒。荣辱判焉。夫孰能挺特奋发。明目张胆。开关键而入堂奥。以化甲为乙。点乙成甲哉。寻常患此。且处下窥高。主张立说。自是至戒。故前书不敢尽言。但请随分讲究。非欲嫌避而尽废资益也。来教谓有当辨而因愚一言止之云。此殆同见疑兵捲甲而守壁。何时能洞开重门。相迎而归也。好笑好笑。致重与之二日开晤。槩见其所存。不但在介然之顷也。惜其沉疴有事不从心处。与愚之所患同也。然同之中。致重。年富资美。在愚则无此二长。愚之患。又深于致重也。别纸所询。无非礼节之难断者。畜书不富。未能博考。何足以知之。略疏愚见于来问之下。汰哉之诮。何得免乎。
存平易气象也。所教较计点装一句。甚善。实地工夫。非较计所存。平易气象。非点装所成。可不惧乎。前书因读穷理之教而言。故曰读书穷理。以体之于身心云云。体之于身心者。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未有穷理而不在敬者。是则曾以为自竭于高明之下矣。今以无相勉为咎。高明于此。或未深察乎。理气说。乃天下正正之公理。人皆可公议。而只为吾东二家。一秦一越。分门割户。传习既久。参错私邪。虽有一言半句。是当究其本。则必以先入。亘在肚里。向前斩断。左袒右袒。荣辱判焉。夫孰能挺特奋发。明目张胆。开关键而入堂奥。以化甲为乙。点乙成甲哉。寻常患此。且处下窥高。主张立说。自是至戒。故前书不敢尽言。但请随分讲究。非欲嫌避而尽废资益也。来教谓有当辨而因愚一言止之云。此殆同见疑兵捲甲而守壁。何时能洞开重门。相迎而归也。好笑好笑。致重与之二日开晤。槩见其所存。不但在介然之顷也。惜其沉疴有事不从心处。与愚之所患同也。然同之中。致重。年富资美。在愚则无此二长。愚之患。又深于致重也。别纸所询。无非礼节之难断者。畜书不富。未能博考。何足以知之。略疏愚见于来问之下。汰哉之诮。何得免乎。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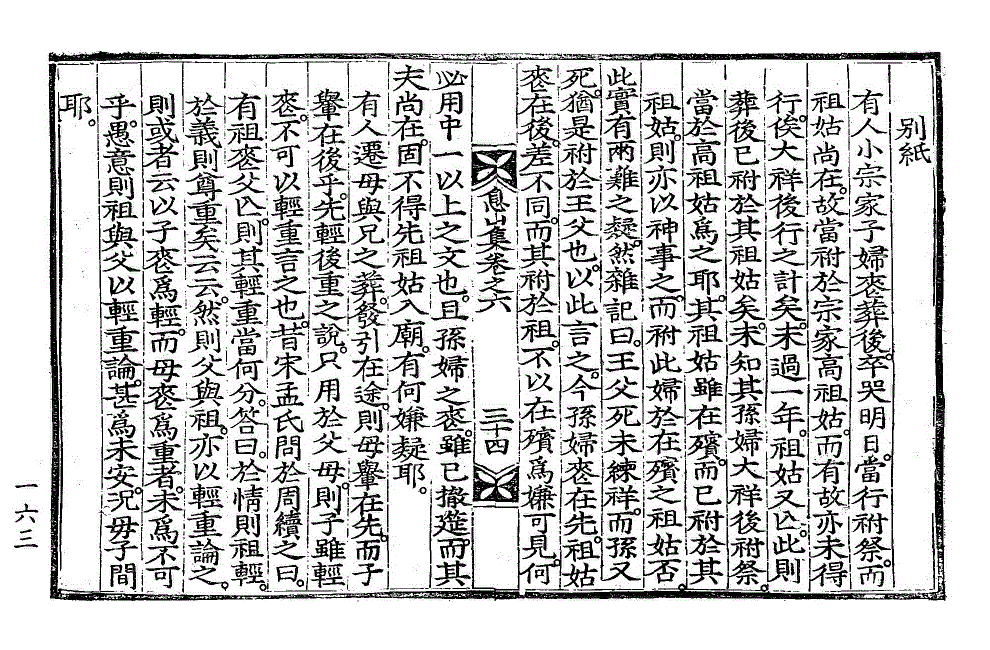 别纸
别纸有人小宗家子妇丧葬后。卒哭明日。当行祔祭。而祖姑尚在。故当祔于宗家高祖姑。而有故亦未得行。俟大祥后行之计矣。未过一年。祖姑又亡。此则葬后已祔于其祖姑矣。未知其孙妇大祥后祔祭。当于高祖姑为之耶。其祖姑虽在殡。而已祔于其祖姑。则亦以神事之。而祔此妇于在殡之祖姑否。
此实有两难之疑。然杂记曰。王父死未练祥。而孙又死。犹是祔于王父也。以此言之。今孙妇丧在先。祖姑丧在后。差不同。而其祔于祖。不以在殡为嫌可见。何必用中一以上之文也。且孙妇之丧。虽已撤筵。而其夫尚在。固不得先祖姑入庙。有何嫌疑耶。
有人迁母与兄之葬。发引在途。则母舆在先。而子舆在后乎。先轻后重之说。只用于父母。则子虽轻丧。不可以轻重言之也。昔宋孟氏问于周续之曰。有祖丧父亡。则其轻重当何分。答曰。于情则祖轻。于义则尊重矣云云。然则父与祖。亦以轻重论之。则或者云以子丧为轻。而母丧为重者。未为不可乎。愚意则祖与父以轻重论。甚为未安。况母子间耶。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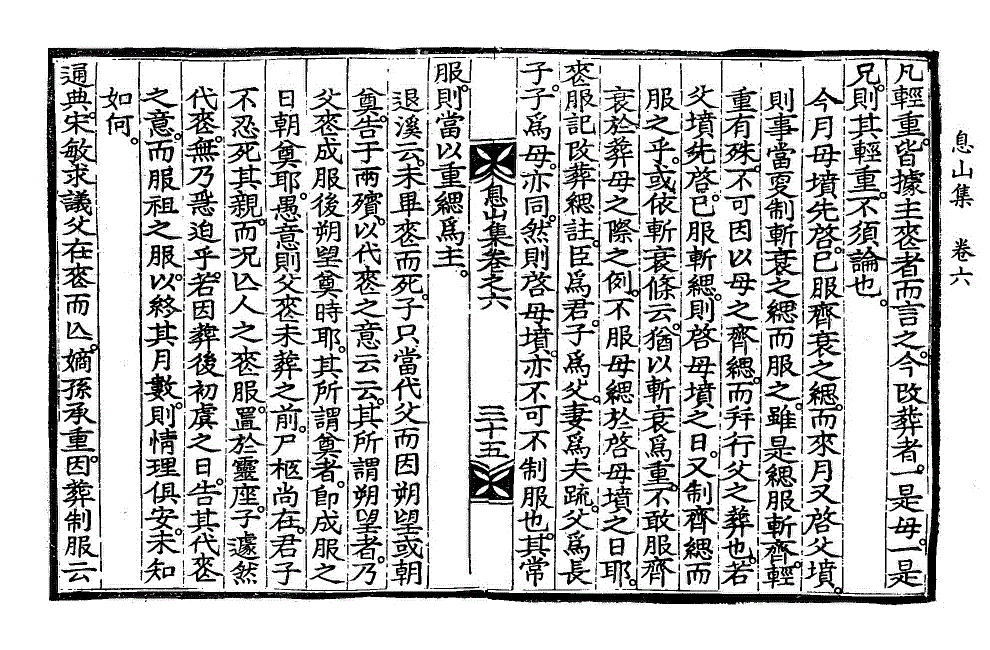 凡轻重。皆据主丧者而言之。今改葬者。一是母。一是兄。则其轻重。不须论也。
凡轻重。皆据主丧者而言之。今改葬者。一是母。一是兄。则其轻重。不须论也。今月母坟先启。已服齐衰之缌。而来月又启父坟。则事当更制斩衰之缌而服之。虽是缌服斩齐。轻重有殊。不可因以母之齐缌。而并行父之葬也。若父坟先启。已服斩缌。则启母坟之日。又制齐缌而服之乎。或依斩衰条云。犹以斩衰为重。不敢服齐衰于葬母之际之例。不服母缌于启母坟之日耶。
丧服记改葬缌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疏。父为长子。子为母。亦同。然则启母坟。亦不可不制服也。其常服。则当以重缌为主。
退溪云。未毕丧而死。子只当代父而因朔望或朝奠。告于两殡。以代丧之意云云。其所谓朔望者。乃父丧成服后朔望奠时耶。其所谓奠者。即成服之日朝奠耶。愚意则父丧未葬之前。尸柩尚在。君子不忍死其亲。而况亡人之丧服。置于灵座。子遽然代丧。无乃急迫乎。若因葬后初虞之日。告其代丧之意。而服祖之服。以终其月数。则情理俱安。未知如何。
通典。宋敏求议父在丧而亡。嫡孙承重。因葬制服云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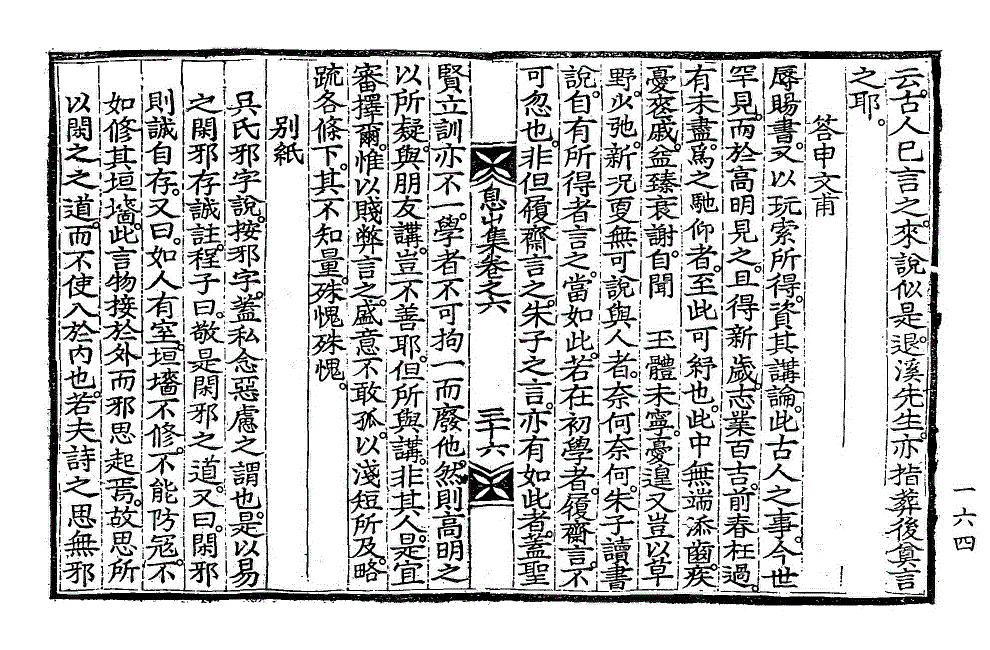 云。古人已言之。来说似是。退溪先生。亦指葬后奠言之耶。
云。古人已言之。来说似是。退溪先生。亦指葬后奠言之耶。答申文甫
辱赐书。又以玩索所得。资其讲论。此古人之事。今世罕见。而于高明见之。且得新岁。志业百吉。前春枉过。有未尽。为之驰仰者。至此可纾也。此中无端添齿。疾忧丧戚。益臻衰谢。自闻 玉体未宁。忧遑又岂以草野。少弛。新况更无可说与人者。奈何奈何。朱子读书说。自有所得者言之。当如此。若在初学者。履斋言。不可忽也。非但履斋言之。朱子之言。亦有如此者。盖圣贤立训亦不一。学者不可拘一而废他。然则高明之以所疑。与朋友讲。岂不善耶。但所与讲。非其人。是宜审择尔。惟以贱弊言之。盛意不敢孤。以浅短所及。略疏各条下。其不知量。殊愧殊愧。
别纸
吴氏邪字说。按邪字。盖私念恶虑之谓也。是以易之闲邪存诚注。程子曰。敬是闲邪之道。又曰。闲邪则诚自存。又曰。如人有室。垣墙不修。不能防寇。不如修其垣墙。此言物接于外而邪思起焉。故思所以闲之之道。而不使入于内也。若夫诗之思无邪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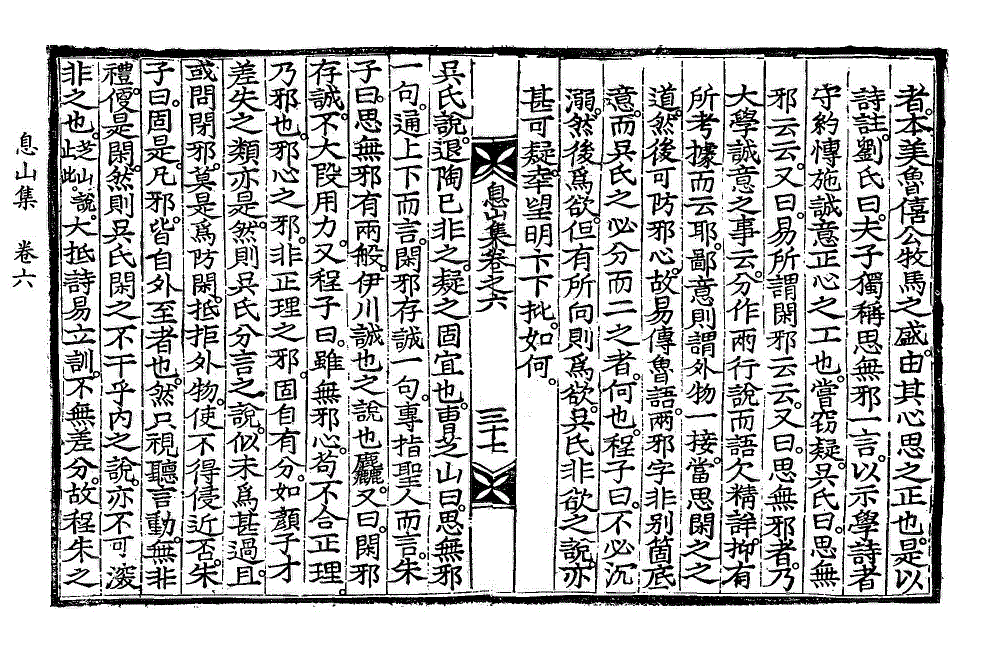 者。本美鲁僖公牧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也。是以诗注。刘氏曰。夫子独称思无邪一言。以示学诗者守约博施诚意正心之工也。尝窃疑。吴氏曰。思无邪云云。又曰。易所谓闲邪云云。又曰。思无邪者。乃大学诚意之事云。分作两行说而语欠精详。抑有所考据而云耶。鄙意则谓外物一接。当思闲之之道。然后可防邪心。故易传鲁语。两邪字非别个底意。而吴氏之必分而二之者。何也。程子曰。不必沉溺。然后为欲。但有所向则为欲。吴氏非欲之说。亦甚可疑。幸望明卞下批。如何。
者。本美鲁僖公牧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也。是以诗注。刘氏曰。夫子独称思无邪一言。以示学诗者守约博施诚意正心之工也。尝窃疑。吴氏曰。思无邪云云。又曰。易所谓闲邪云云。又曰。思无邪者。乃大学诚意之事云。分作两行说而语欠精详。抑有所考据而云耶。鄙意则谓外物一接。当思闲之之道。然后可防邪心。故易传鲁语。两邪字非别个底意。而吴氏之必分而二之者。何也。程子曰。不必沉溺。然后为欲。但有所向则为欲。吴氏非欲之说。亦甚可疑。幸望明卞下批。如何。吴氏说。退陶已非之。疑之固宜也。曹芝山曰。思无邪一句。通上下而言。闲邪存诚一句。专指圣人而言。朱子曰。思无邪有两般。伊川诚也之说也粗。又曰。闲邪存诚。不大段用力。又程子曰。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也。邪心之邪。非正理之邪。固自有分。如颜子才差失之类亦是。然则吴氏分言之说。似未为甚过。且或问闭邪。莫是为防闲。抵拒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朱子曰。固是。凡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视听言动。无非礼。便是闲。然则吴氏闲之不干乎内之说。亦不可深非之也。(芝山说。止此。)大抵诗易立训。不无差分。故程朱之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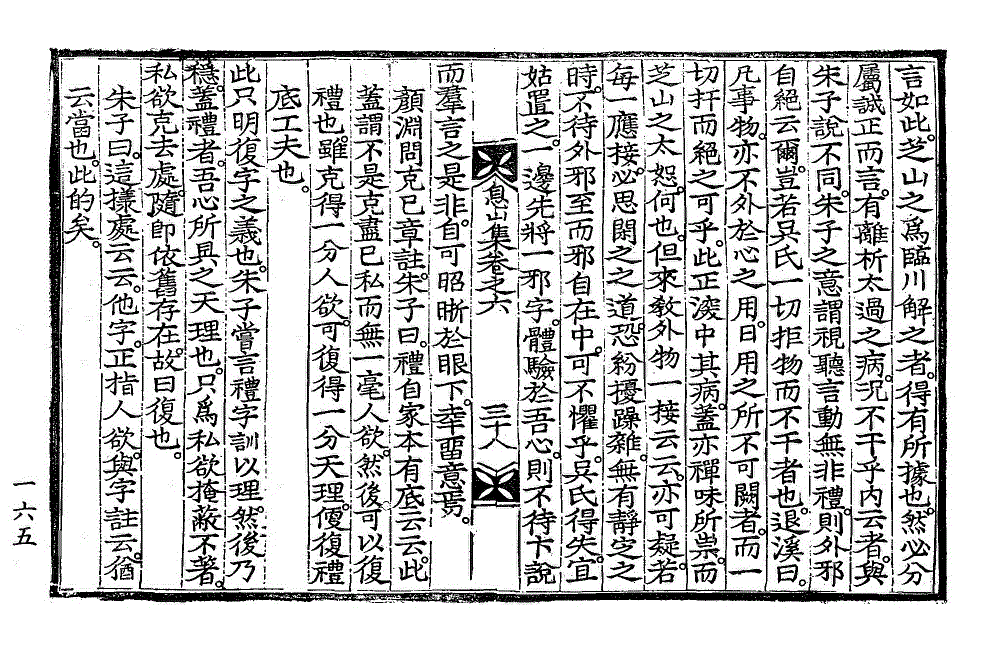 言如此。芝山之为临川解之者。得有所据也。然必分属诚正而言。有离析太过之病。况不干乎内云者。与朱子说不同。朱子之意谓视听言动无非礼。则外邪自绝云尔。岂若吴氏一切拒物而不干者也。退溪曰。凡事物。亦不外于心之用。日用之所不可阙者。而一切捍而绝之可乎。此正深中其病。盖亦禅味所祟。而芝山之太恕。何也。但来教外物一接云云。亦可疑。若每一应接。必思闲之之道。恐纷扰躁杂。无有静定之时。不待外邪至而邪自在中。可不惧乎。吴氏得失。宜姑置之。一边先将一邪字。体验于吾心。则不待卞说而群言之是非。自可昭晢于眼下。幸留意焉。
言如此。芝山之为临川解之者。得有所据也。然必分属诚正而言。有离析太过之病。况不干乎内云者。与朱子说不同。朱子之意谓视听言动无非礼。则外邪自绝云尔。岂若吴氏一切拒物而不干者也。退溪曰。凡事物。亦不外于心之用。日用之所不可阙者。而一切捍而绝之可乎。此正深中其病。盖亦禅味所祟。而芝山之太恕。何也。但来教外物一接云云。亦可疑。若每一应接。必思闲之之道。恐纷扰躁杂。无有静定之时。不待外邪至而邪自在中。可不惧乎。吴氏得失。宜姑置之。一边先将一邪字。体验于吾心。则不待卞说而群言之是非。自可昭晢于眼下。幸留意焉。颜渊问克己章注。朱子曰。礼自家本有底云云。此盖谓不是克尽己私而无一毫人欲。然后。可以复礼也。虽克得一分人欲。可复得一分天理。便复礼底工夫也。
此只明复字之义也。朱子尝言礼字训以理。然后乃稳。盖礼者。吾心所具之天理也。只为私欲掩蔽不著。私欲克去处。随即依旧存在。故曰复也。
朱子曰。这㨾处云云。他字。正指人欲。与字注云。犹云当也。此的矣。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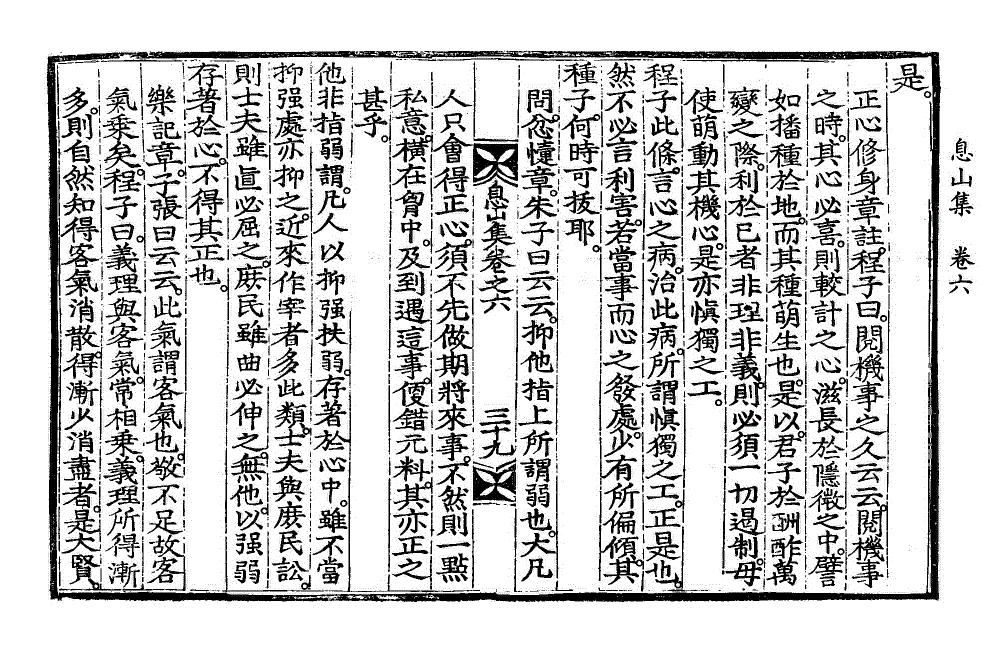 是。
是。正心修身章注。程子曰。阅机事之久云云。阅机事之时。其心必喜。则较计之心。滋长于隐微之中。譬如播种于地。而其种萌生也。是以。君子于酬酢万变之际。利于己者非理非义。则必须一切遏制。毋使萌动其机心。是亦慎独之工。
程子此条。言心之病。治此病。所谓慎独之工。正是也。然不必言利害。若当事而心之发处。少有所偏倾。其种子。何时可拔耶。
问。忿懥章。朱子曰云云。抑他指上所谓弱也。大凡人只会得正心。须不先做期将来事。不然则一点私意。横在胸中。及到遇这事。便错元料。其亦正之甚乎。
他非指弱谓。凡人以抑强扶弱。存著于心中。虽不当抑强处亦抑之。近来作宰者多此类。士夫与庶民讼。则士夫虽直必屈之。庶民虽曲必伸之。无他。以强弱存著于心。不得其正也。
乐记章。子张曰云云。此气谓客气也。敬不足故客气乘矣。程子曰。义理与客气。常相乘。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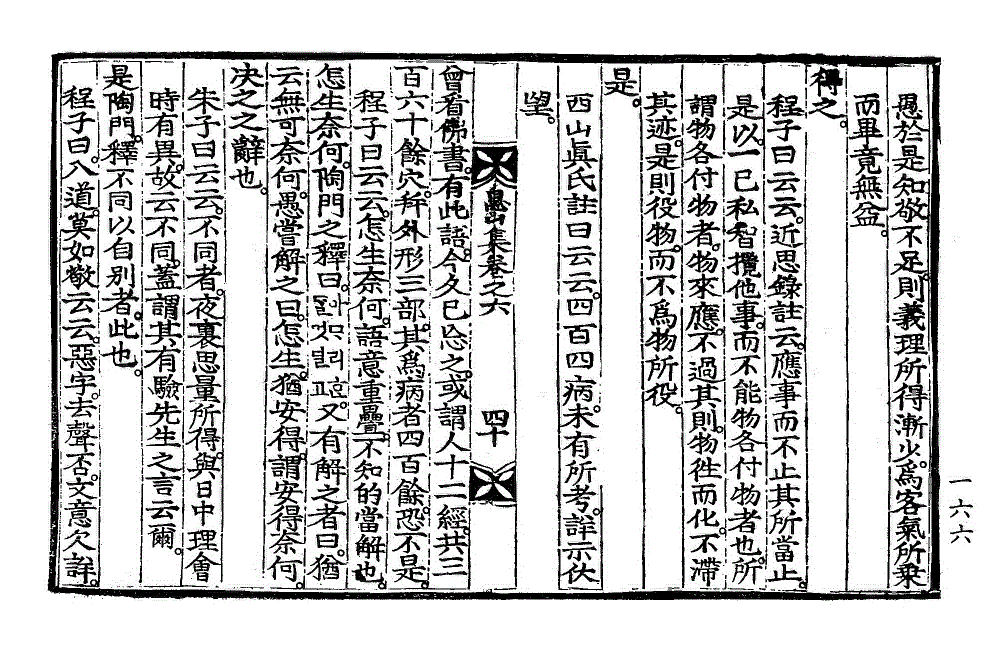 愚于是知敬不足。则义理所得渐少。为客气所乘而毕竟无益。
愚于是知敬不足。则义理所得渐少。为客气所乘而毕竟无益。得之。
程子曰云云。近思录注云。应事而不止其所当止。是以。一己私智揽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谓物各付物者。物来应。不过其则。物往而化。不滞其迹。是则役物。而不为物所役。
是。
西山真氏注曰云云。四百四病。未有所考。详示伏望。
曾看佛书。有此语。今久已忘之。或谓人十二经。共三百六十馀穴。并外形三部。其为病者四百馀。恐不是。
程子曰云云。怎生奈何。语意重叠。不知的当解也。
怎生奈何。陶门之释曰。(아리엇딜고。)又有解之者曰。犹云无可奈何。愚尝解之曰。怎生。犹安得。谓安得奈何。决之之辞也。
朱子曰云云。不同者。夜里思量所得。与日中理会时有异。故云不同。盖谓其有验先生之言云尔。
是陶门。释不同以自别者。此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云云。恶字。去声否。文意欠详。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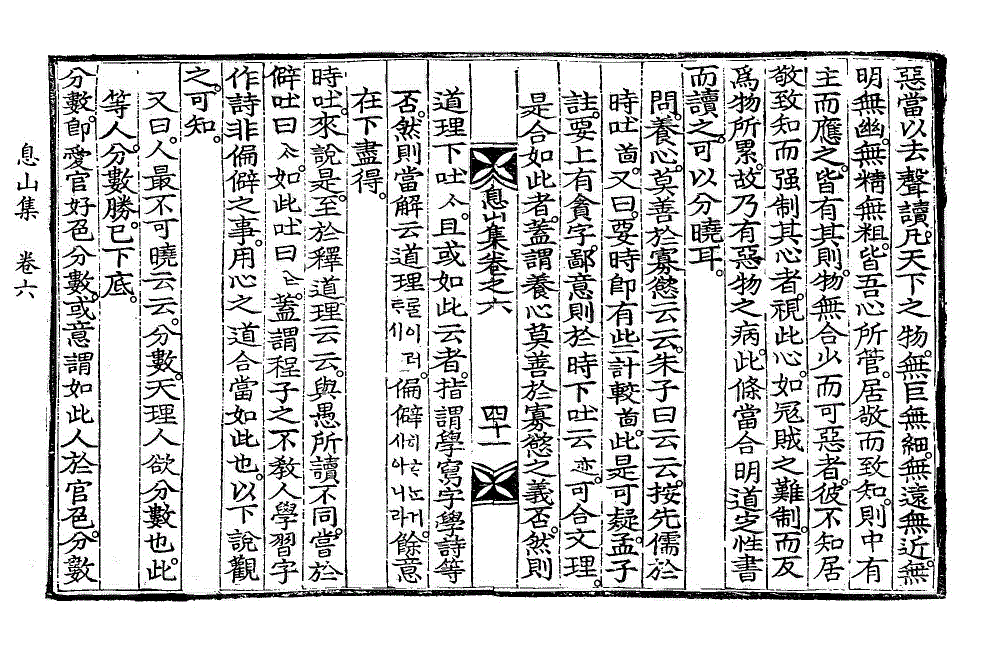 恶当以去声读。凡天下之物。无巨无细。无远无近。无明无幽。无精无粗。皆吾心所管。居敬而致知。则中有主而应之。皆有其则。物无合少而可恶者。彼不知居敬致知而强制其心者。视此心。如寇贼之难制。而反为物所累。故乃有恶物之病。此条当合明道定性书而读之。可以分晓耳。
恶当以去声读。凡天下之物。无巨无细。无远无近。无明无幽。无精无粗。皆吾心所管。居敬而致知。则中有主而应之。皆有其则。物无合少而可恶者。彼不知居敬致知而强制其心者。视此心。如寇贼之难制。而反为物所累。故乃有恶物之病。此条当合明道定性书而读之。可以分晓耳。问。养心。莫善于寡欲云云。朱子曰云云。按先儒于时吐。又曰。要时即有些计较。此是可疑。孟子注。要上有贪字。鄙意则于时下吐云。可合文理。是合如此者。盖谓养心莫善于寡欲之义否。然则道理下吐。且或如此云者。指谓学写字学诗等否。然则当解云道理(이러시)。偏僻(히거시아니라)。馀意在下尽得。
时吐。来说是。至于释道理云云。与愚所读不同。尝于僻吐曰。如此吐曰。盖谓程子之不教人学习字作诗非偏僻之事。用心之道合当如此也。以下说观之。可知。
又曰。人最不可晓云云。分数。天理人欲分数也。此等人。分数胜。已下底。
分数。即爱官好色分数。或意谓如此人于官色。分数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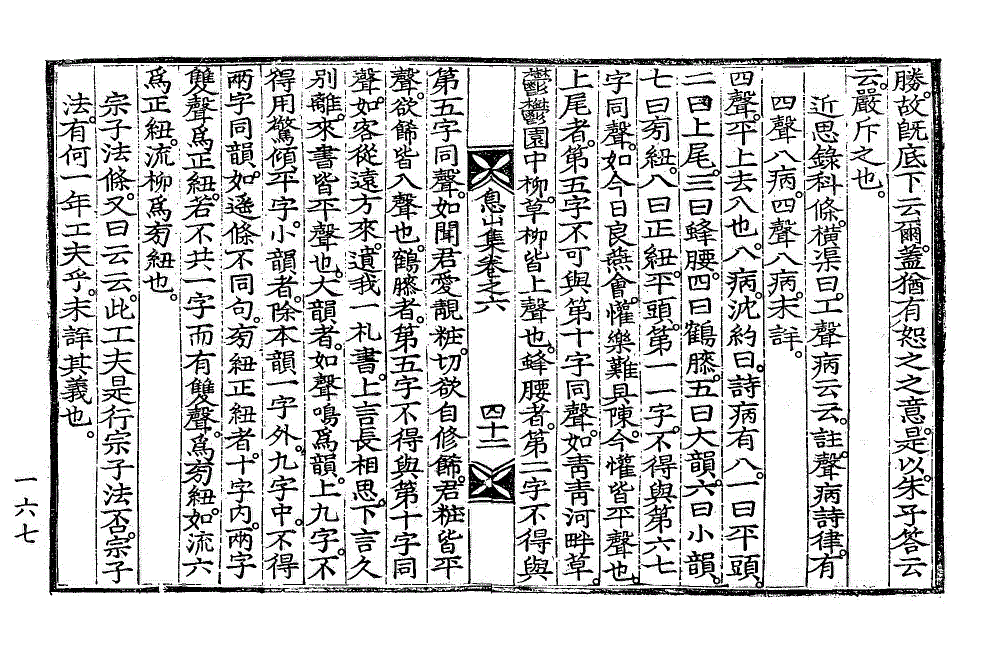 胜。故既底下云尔。盖犹有恕之之意。是以。朱子答云云。严斥之也。
胜。故既底下云尔。盖犹有恕之之意。是以。朱子答云云。严斥之也。近思录科条。横渠曰。工声病云云。注。声病诗律。有四声八病。四声八病。未详。
四声。平上去入也。八病。沈约曰。诗病有八。一曰平头。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鹤膝。五曰大韵。六曰小韵。七曰旁纽。八曰正纽。平头。第一一字。不得与第六七字同声。如今日良燕会。欢乐难具陈。今欢皆平声也。上尾者。第五字不可与第十字同声。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皆上声也。蜂腰者。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如闻君爱靓妆。切欲自修饰。君妆皆平声。欲饰皆入声也。鹤膝者。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札书。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来书皆平声也。大韵者。如声鸣为韵。上九字。不得用惊倾平字。小韵者。除本韵一字外。九字中。不得两字同韵。如遥条不同句。旁纽正纽者。十字内。两字双声为正纽。若不共一字而有双声。为旁纽。如流六为正纽。流柳为旁纽也。
宗子法条。又曰云云。此工夫是行宗子法否。宗子法。有何一年工夫乎。未详其义也。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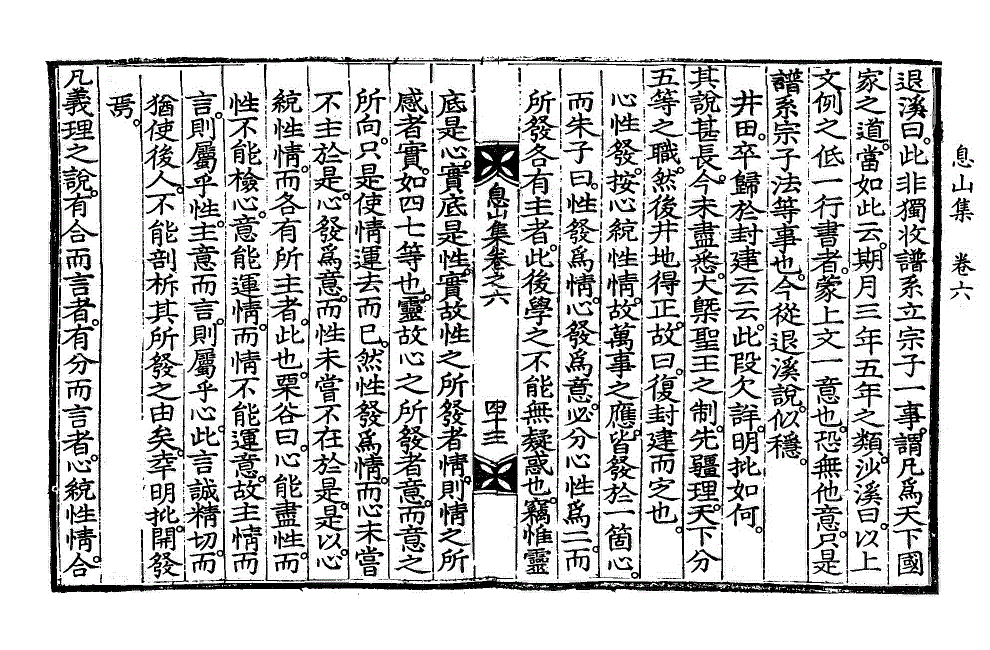 退溪曰。此非独收谱系立宗子一事。谓凡为天下国家之道。当如此云。期月三年五年之类。沙溪曰。以上文例之低一行书者。蒙上文一意也。恐无他意。只是谱系宗子法等事也。今从退溪说。似稳。
退溪曰。此非独收谱系立宗子一事。谓凡为天下国家之道。当如此云。期月三年五年之类。沙溪曰。以上文例之低一行书者。蒙上文一意也。恐无他意。只是谱系宗子法等事也。今从退溪说。似稳。井田。卒归于封建云云。此段欠详。明批如何。
其说甚长。今未尽悉。大槩圣王之制。先疆理。天下分五等之职。然后井地得正。故曰。复封建而定也。
心性发。按心统性情。故万事之应。皆发于一个心。而朱子曰。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必分心性为二。而所发各有主者。此后学之不能无疑惑也。窃惟灵底是心。实底是性。实故性之所发者情。则情之所感者实。如四七等也。灵故心之所发者意。而意之所向。只是使情运去而已。然性发为情。而心未尝不主于是。心发为意。而性未尝不在于是。是以。心统性情。而各有所主者。此也。栗谷曰。心能尽性。而性不能检心。意能运情。而情不能运意。故主情而言。则属乎性。主意而言。则属乎心。此言诚精切。而犹使后人。不能剖析其所发之由矣。幸明批。开发焉。
凡义理之说。有合而言者。有分而言者。心统性情。合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8L 页
 言之言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分言之言也。然合不害于其分。分不害于其合。槩言心则性情意。俱为其所包。而情因所感迭出。其本色不易者。何也。以自性中所具透来。如具仁而为恻隐。具义而为羞恶之类。是也。意因其所感之机。为之裁度不齐者。何也。以自心中神明拖来。如仁则度如何为仁。义则度如何为义之类。是也。此其所分可见。虽然。情因心而受于性。意自心而缘于情。心之统领。亦依旧。此其所合。亦可见。所谓分合不害者益明矣。
言之言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分言之言也。然合不害于其分。分不害于其合。槩言心则性情意。俱为其所包。而情因所感迭出。其本色不易者。何也。以自性中所具透来。如具仁而为恻隐。具义而为羞恶之类。是也。意因其所感之机。为之裁度不齐者。何也。以自心中神明拖来。如仁则度如何为仁。义则度如何为义之类。是也。此其所分可见。虽然。情因心而受于性。意自心而缘于情。心之统领。亦依旧。此其所合。亦可见。所谓分合不害者益明矣。答申文甫
前送复。闻久滞未传。谓终得尘清案。早晚何伤也。续承崇札。知已得彻。所对诸说。亦少挥斥。妄言之罪。快得容贷。感荷无量。更知静况安胜。尤可贺也。仆早春齿病。向暖少减。复以所居茅庵。意外回禄。不得不修刱。穷家当春经纪。令人汩没。近始苟完。吴敬止两子丁德。而两子及他家子弟。聚居诵读。日日所讲。皆圣贤言语。古人文字。心专在此。虽无他歧。然同处者。皆少年蒙学。绝无警发之益。是可叹也。致重遭巨创。念其清羸抱疾。有难生全。况其家稀世之庆。未及设席。有此变故。祸福相寻。乃如此。可慨也。别纸所示。益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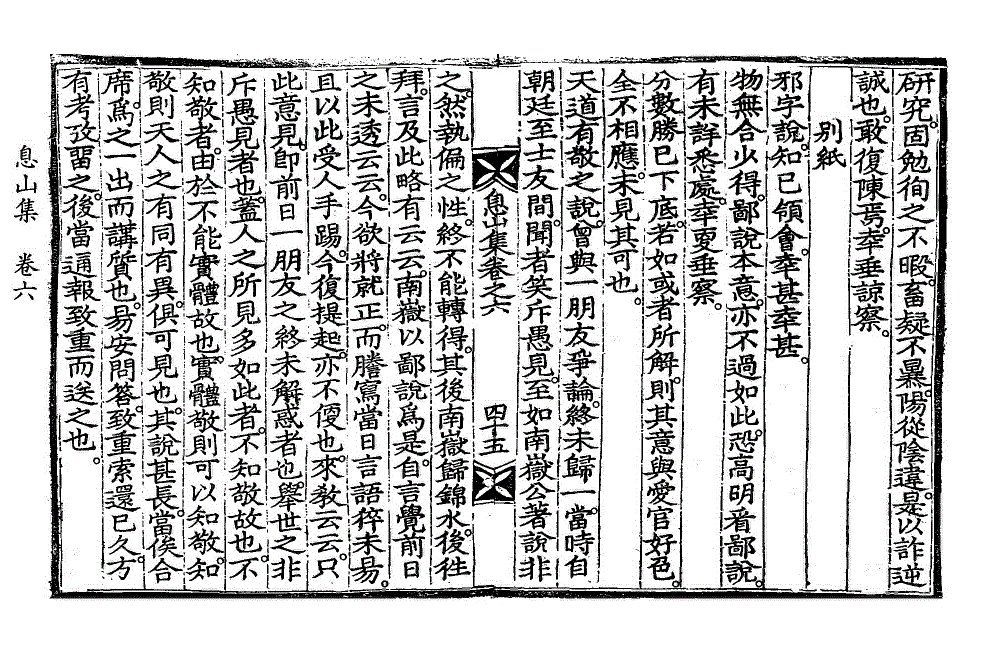 研究。固勉徇之不暇。畜疑不▼(日/出/恭)。阳从阴违。是以诈逆诚也。敢复陈焉。幸垂谅察。
研究。固勉徇之不暇。畜疑不▼(日/出/恭)。阳从阴违。是以诈逆诚也。敢复陈焉。幸垂谅察。别纸
邪字说。知已领会。幸甚幸甚。
物无合少得。鄙说本意。亦不过如此。恐高明看鄙说。有未详悉处。幸更垂察。
分数胜已下底。若如或者所解。则其意与爱官好色。全不相应。未见其可也。
天道有敬之说。曾与一朋友争论。终未归一。当时自朝廷至士友间。闻者笑斥愚见。至如南岳公著说非之。然执偏之性。终不能转得。其后南岳归锦水。后往拜。言及此略有云云。南岳以鄙说为是。自言觉前日之未透云云。今欲将就正。而誊写当日言语猝未易。且以此受人手踢。今复提起。亦不便也。来教云云。只此意见。即前日一朋友之终未解惑者也。举世之非斥愚见者也。盖人之所见多如此者。不知敬故也。不知敬者。由于不能实体故也。实体敬则可以知敬。知敬则天人之有同有异。俱可见也。其说甚长。当俟合席。为之一出而讲质也。易安问答。致重索还已久。方有考考留之。后当通报致重而送之也。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9L 页
 答申文甫
答申文甫一字连虚灵知觉而言。何必挨至理乎。两心虽非有两本相对而出。然岂可曰。出于一理也。既云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不可以一之甚明。大抵虚所以为体也。灵所以为用也。虚灵故知觉。知觉正是心之发处。而其所向不同。故有道人之分。朱子曰。一心。知觉从耳目上去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是道心。又曰。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以此观之。其分界甚明。无可疑者。若如来说。理中元有挟杂。两心同出。既背朱子之意。程,张气质之说。亦无所用也。
答申文甫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谓心之神明。于性命形气上。非有两㨾知觉。故曰一也。以其有人心道心之异者。知觉一矣。而心有二名者。正为有原于性命者。有生于形气者。故曰异也。
来教所谓一异字相应者。固是也。然其所以应如何。不过这个一而那个异也。这个。即知觉者也。那个。即知觉处也。知觉处不同。则其所以分。可知也。然则愚所谓相应者。一而异也。高明所谓相应者。异而欲一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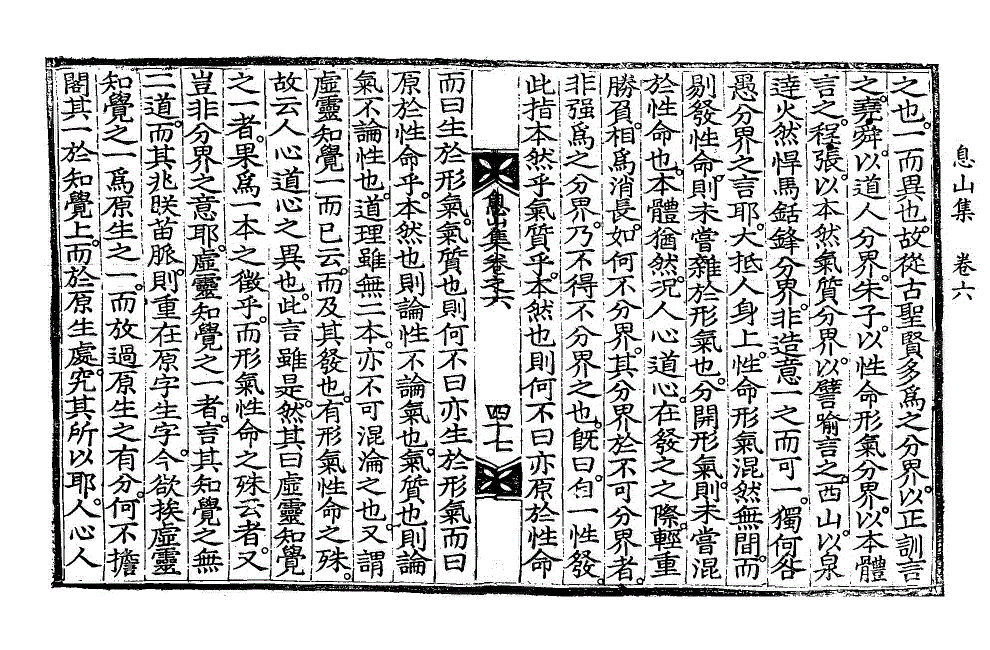 之也。一而异也。故从古圣贤多为之分界。以正训言之。尧,舜。以道人分界。朱子。以性命形气分界。以本体言之。程,张。以本然气质分界。以譬喻言之。西山。以泉达火然悍马铦锋分界。非造意一之而可一。独何咎愚分界之言耶。大抵人身上。性命形气混然无间。而剔发性命。则未尝杂于形气也。分开形气。则未尝混于性命也。本体犹然。况人心道心。在发之之际。轻重胜负。相为消长。如何不分界。其分界于不可分界者。非强为之分界。乃不得不分界之也。既曰。自一性发。此指本然乎气质乎。本然也则何不曰亦原于性命而曰生于形气。气质也则何不曰亦生于形气而曰原于性命乎。本然也则论性不论气也。气质也则论气不论性也。道理虽无二本。亦不可混沦之也。又谓虚灵知觉一而已云。而及其发也。有形气性命之殊。故云人心道心之异也。此言虽是。然其曰虚灵知觉之一者。果为一本之徵乎。而形气性命之殊云者。又岂非分界之意耶。虚灵知觉之一者。言其知觉之无二道。而其兆眹苗脉。则重在原字生字。今欲挨虚灵知觉之一为原生之一。而放过原生之有分。何不担阁其一于知觉上。而于原生处。究其所以耶。人心人
之也。一而异也。故从古圣贤多为之分界。以正训言之。尧,舜。以道人分界。朱子。以性命形气分界。以本体言之。程,张。以本然气质分界。以譬喻言之。西山。以泉达火然悍马铦锋分界。非造意一之而可一。独何咎愚分界之言耶。大抵人身上。性命形气混然无间。而剔发性命。则未尝杂于形气也。分开形气。则未尝混于性命也。本体犹然。况人心道心。在发之之际。轻重胜负。相为消长。如何不分界。其分界于不可分界者。非强为之分界。乃不得不分界之也。既曰。自一性发。此指本然乎气质乎。本然也则何不曰亦原于性命而曰生于形气。气质也则何不曰亦生于形气而曰原于性命乎。本然也则论性不论气也。气质也则论气不论性也。道理虽无二本。亦不可混沦之也。又谓虚灵知觉一而已云。而及其发也。有形气性命之殊。故云人心道心之异也。此言虽是。然其曰虚灵知觉之一者。果为一本之徵乎。而形气性命之殊云者。又岂非分界之意耶。虚灵知觉之一者。言其知觉之无二道。而其兆眹苗脉。则重在原字生字。今欲挨虚灵知觉之一为原生之一。而放过原生之有分。何不担阁其一于知觉上。而于原生处。究其所以耶。人心人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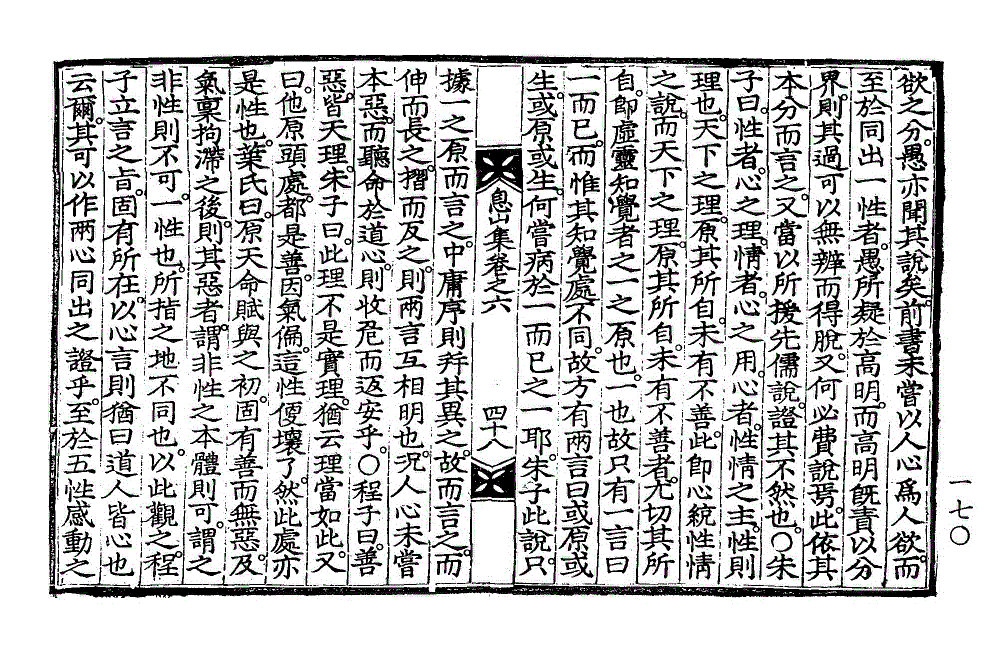 欲之分。愚亦闻其说矣。前书未尝以人心为人欲。而至于同出一性者。愚所疑于高明。而高明既责以分界。则其过可以无辨而得脱。又何必费说焉。此依其本分而言之。又当以所援先儒说。證其不然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则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此即心统性情之说。而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者。尤切其所自。即虚灵知觉者之一之原也。一也故只有一言曰一而已。而惟其知觉处不同。故方有两言曰或原或生。或原或生。何尝病于一而已之一耶。朱子此说。只据一之原而言之。中庸序则并其异之。故而言之。而伸而长之。摺而反之。则两言互相明也。况人心未尝本恶。而听命于道心。则收危而返安乎。○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朱子曰。此理不是实理。犹云理当如此。又曰。他原头处。都是善。因气偏。这性便坏了。然此处亦是性也。叶氏曰。原天命赋与之初。固有善而无恶。及气禀拘滞之后。则其恶者。谓非性之本体则可。谓之非性则不可。一性也。所指之地不同也。以此观之。程子立言之旨。固有所在。以心言则犹曰道人皆心也云尔。其可以作两心同出之證乎。至于五性感动之
欲之分。愚亦闻其说矣。前书未尝以人心为人欲。而至于同出一性者。愚所疑于高明。而高明既责以分界。则其过可以无辨而得脱。又何必费说焉。此依其本分而言之。又当以所援先儒说。證其不然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则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此即心统性情之说。而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者。尤切其所自。即虚灵知觉者之一之原也。一也故只有一言曰一而已。而惟其知觉处不同。故方有两言曰或原或生。或原或生。何尝病于一而已之一耶。朱子此说。只据一之原而言之。中庸序则并其异之。故而言之。而伸而长之。摺而反之。则两言互相明也。况人心未尝本恶。而听命于道心。则收危而返安乎。○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朱子曰。此理不是实理。犹云理当如此。又曰。他原头处。都是善。因气偏。这性便坏了。然此处亦是性也。叶氏曰。原天命赋与之初。固有善而无恶。及气禀拘滞之后。则其恶者。谓非性之本体则可。谓之非性则不可。一性也。所指之地不同也。以此观之。程子立言之旨。固有所在。以心言则犹曰道人皆心也云尔。其可以作两心同出之證乎。至于五性感动之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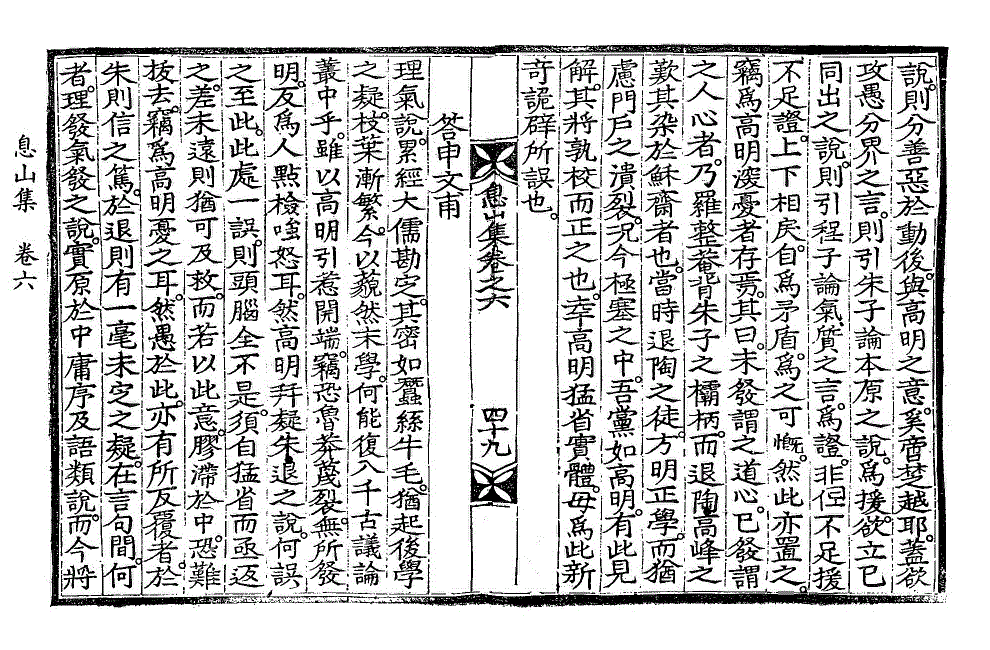 说。则分善恶于动后。与高明之意。奚啻楚越耶。盖欲攻愚分界之言。则引朱子论本原之说。为援。欲立己同出之说。则引程子论气质之言。为證。非但不足援不足證。上下相戾。自为矛盾。为之可慨。然此亦置之。窃为高明深忧者存焉。其曰。未发谓之道心。已发谓之人心者。乃罗整庵背朱子之把柄。而退陶,高峰之叹其染于稣斋者也。当时退陶之徒。方明正学。而犹虑门户之溃裂。况今极塞之中。吾党如高明。有此见解。其将孰校而正之也。幸高明猛省实体。毋为此新奇诡辟所误也。
说。则分善恶于动后。与高明之意。奚啻楚越耶。盖欲攻愚分界之言。则引朱子论本原之说。为援。欲立己同出之说。则引程子论气质之言。为證。非但不足援不足證。上下相戾。自为矛盾。为之可慨。然此亦置之。窃为高明深忧者存焉。其曰。未发谓之道心。已发谓之人心者。乃罗整庵背朱子之把柄。而退陶,高峰之叹其染于稣斋者也。当时退陶之徒。方明正学。而犹虑门户之溃裂。况今极塞之中。吾党如高明。有此见解。其将孰校而正之也。幸高明猛省实体。毋为此新奇诡辟所误也。答申文甫
理气说。累经大儒勘定。其密如蚕丝牛毛。犹起后学之疑。枝叶渐繁。今以藐然末学。何能复入千古议论丛中乎。虽以高明引惹开端。窃恐鲁莽蔑裂。无所发明。反为人点检嗤怒耳。然高明并疑朱,退之说。何误之至此。此处一误。则头脑全不是。须自猛省而亟返之。差未远则犹可及救。而若以此意。胶滞于中。恐难拔去。窃为高明忧之耳。然愚于此。亦有所反覆者。于朱则信之笃。于退则有一毫未定之疑。在言句间。何者。理发气发之说。实原于中庸序及语类说。而今将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1L 页
 三言消详之。原者。谓原于性命而发。非性命直发也。生者谓感于形气而生。非形气直生也。理之发气之发。亦谓理之所发。气之所发。非理气直发也。盖人心有觉于义理上时。有觉于形气上时。其觉于义理之心。岂非原于性命之理之发乎。觉于形气之心。岂非感于形气之气之生乎。若直云理发气发。则是似理气直发。理气直发云。则易至于两本各出。是则于之二字斡旋。其义趣有所自别。然老先生一言一动。无不本于紫阳。岂于此有失其旨者哉。况以气随理乘。足其下。其意可见。学者。当以意逆志。不以辞害义。可也。至于栗谷。则极力驱退于两本之误。而无少敬逊之意。所自为说。张皇支离。又欲掩朱而自立。似欠和易知道者气象。未论义理之前。已可觑破其所成就如何耳。然欲辨言得失。则其说甚长。猝难得也。但于日用切近处。慎言慎行。待其见益精明。从违自定。不须乍看影子。径以说句断。可也。
三言消详之。原者。谓原于性命而发。非性命直发也。生者谓感于形气而生。非形气直生也。理之发气之发。亦谓理之所发。气之所发。非理气直发也。盖人心有觉于义理上时。有觉于形气上时。其觉于义理之心。岂非原于性命之理之发乎。觉于形气之心。岂非感于形气之气之生乎。若直云理发气发。则是似理气直发。理气直发云。则易至于两本各出。是则于之二字斡旋。其义趣有所自别。然老先生一言一动。无不本于紫阳。岂于此有失其旨者哉。况以气随理乘。足其下。其意可见。学者。当以意逆志。不以辞害义。可也。至于栗谷。则极力驱退于两本之误。而无少敬逊之意。所自为说。张皇支离。又欲掩朱而自立。似欠和易知道者气象。未论义理之前。已可觑破其所成就如何耳。然欲辨言得失。则其说甚长。猝难得也。但于日用切近处。慎言慎行。待其见益精明。从违自定。不须乍看影子。径以说句断。可也。答金大集(圣运)
风便寄问。亦不容易。今委价半千寒程。高义令人钦叹。玩弄清泚。依前佳胜。尤可耸想。服人自来尘土物。随分饮啄。存殁恼心。抚时增感。愧向清净界。道此苦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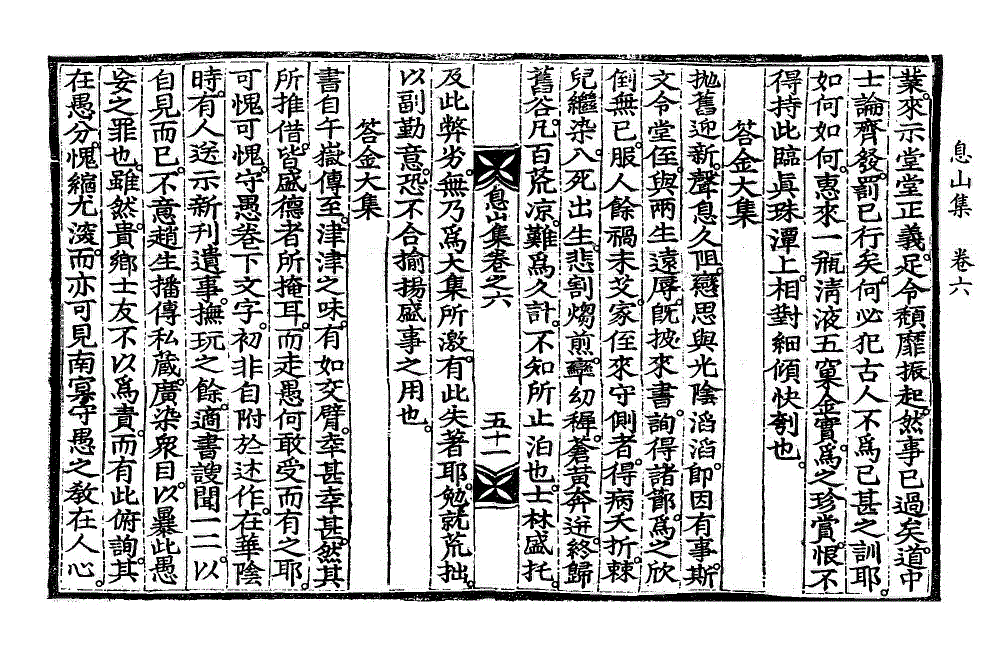 业。来示堂堂正义。足令颓靡振起。然事已过矣。道中士论齐发。罚已行矣。何必犯古人不为已甚之训耶。如何如何。惠来一瓶清液五窠金实。为之珍赏。恨不得持此临真珠潭上。相对细倾快刳也。
业。来示堂堂正义。足令颓靡振起。然事已过矣。道中士论齐发。罚已行矣。何必犯古人不为已甚之训耶。如何如何。惠来一瓶清液五窠金实。为之珍赏。恨不得持此临真珠潭上。相对细倾快刳也。答金大集
抛旧迎新。声息久阻。恋思与光阴滔滔。即因有事。斯文令堂侄。与两生远辱。既披来书。询得诸节。为之欣倒无已。服人馀祸未艾。家侄来守侧者。得病夭折。棘儿继染。入死出生。悲割煼煎。率幼稚。苍黄奔迸。终归旧谷。凡百荒凉。难为久计。不知所止泊也。士林盛托。及此弊劣。无乃为大集所激。有此失著耶。勉就荒拙。以副勤意。恐不合揄扬盛事之用也。
答金大集
书自午岳传至。津津之味。有如交臂。幸甚幸甚。然其所推借。皆盛德者所掩耳。而走愚何敢受而有之耶。可愧可愧。守愚卷下文字。初非自附于述作。在华阴时。有人送示新刊遗事。抚玩之馀。适书謏闻一二。以自见而已。不意赵生播传私藏。广染众目。以▼(日/出/恭)此愚妄之罪也。虽然。贵乡士友不以为责。而有此俯询。其在愚分。愧缩尤深。而亦可见南冥,守愚之教在人心。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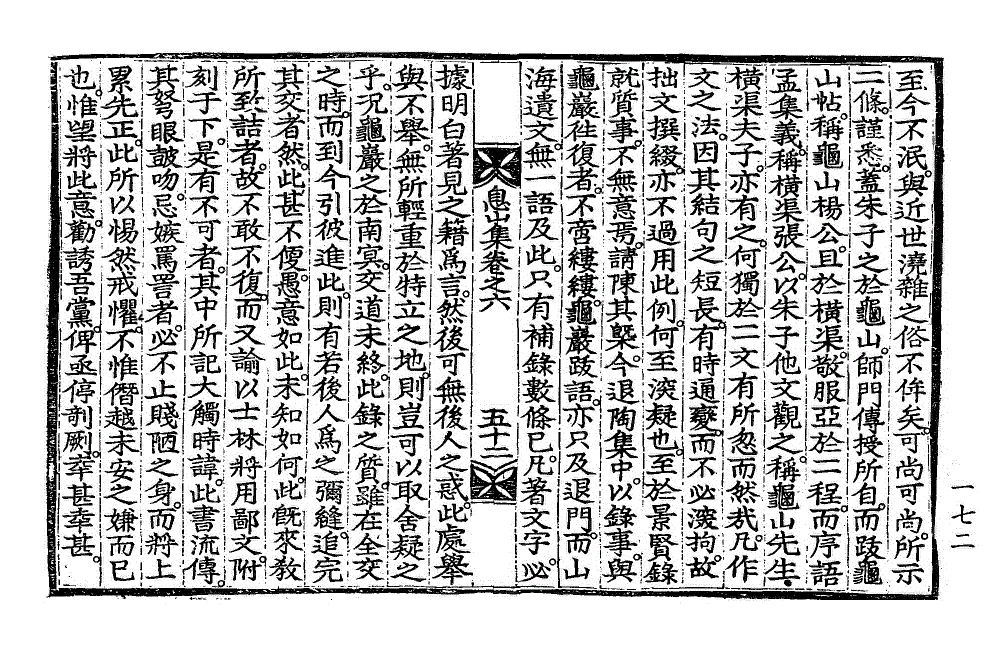 至今不泯。与近世浇杂之俗不侔矣。可尚可尚。所示二条。谨悉。盖朱子之于龟山。师门传授所自。而跋龟山帖。称龟山杨公。且于横渠。敬服亚于二程。而序语孟集义。称横渠张公。以朱子他文观之。称龟山先生,横渠夫子。亦有之。何独于二文有所忽而然哉。凡作文之法。因其结句之短长。有时通变。而不必深拘。故拙文撰缀。亦不过用此例。何至深疑也。至于景贤录就质事。不无意焉。请陈其槩。今退陶集中。以录事。与龟岩往复者。不啻缕缕。龟岩跋语。亦只及退门。而山海遗文。无一语及此。只有补录数条已。凡著文字。必据明白著见之籍为言。然后可无后人之惑。此处举与不举。无所轻重于特立之地。则岂可以取舍疑之乎。况龟岩之于南冥。交道未终。此录之质。虽在全交之时。而到今引彼进此。则有若后人为之弥缝。追完其交者然。此甚不便。愚意如此。未知如何。此既来教所致诘者。故不敢不复。而又谕以士林将用鄙文。附刻于下。是有不可者。其中所记大触时讳。此书流传。其弩眼鼓吻。忌嫉骂詈者。必不止贱陋之身。而将上累先正。此所以惕然戒惧。不惟僭越未安之嫌而已也。惟望将此意。劝诱吾党。俾亟停剞劂。幸甚幸甚。
至今不泯。与近世浇杂之俗不侔矣。可尚可尚。所示二条。谨悉。盖朱子之于龟山。师门传授所自。而跋龟山帖。称龟山杨公。且于横渠。敬服亚于二程。而序语孟集义。称横渠张公。以朱子他文观之。称龟山先生,横渠夫子。亦有之。何独于二文有所忽而然哉。凡作文之法。因其结句之短长。有时通变。而不必深拘。故拙文撰缀。亦不过用此例。何至深疑也。至于景贤录就质事。不无意焉。请陈其槩。今退陶集中。以录事。与龟岩往复者。不啻缕缕。龟岩跋语。亦只及退门。而山海遗文。无一语及此。只有补录数条已。凡著文字。必据明白著见之籍为言。然后可无后人之惑。此处举与不举。无所轻重于特立之地。则岂可以取舍疑之乎。况龟岩之于南冥。交道未终。此录之质。虽在全交之时。而到今引彼进此。则有若后人为之弥缝。追完其交者然。此甚不便。愚意如此。未知如何。此既来教所致诘者。故不敢不复。而又谕以士林将用鄙文。附刻于下。是有不可者。其中所记大触时讳。此书流传。其弩眼鼓吻。忌嫉骂詈者。必不止贱陋之身。而将上累先正。此所以惕然戒惧。不惟僭越未安之嫌而已也。惟望将此意。劝诱吾党。俾亟停剞劂。幸甚幸甚。答金大集
秋来一札。可见相思之心。山中。霜后绣屏。日可酣玩。竹檐低开新酿。用大白快倾。想风味甚奇。恨不得翼入祥树下。如前年事也。鄙拙还旧寓。值此大杀。悔不用故人忠谋。乃受此生受也。奈何奈何。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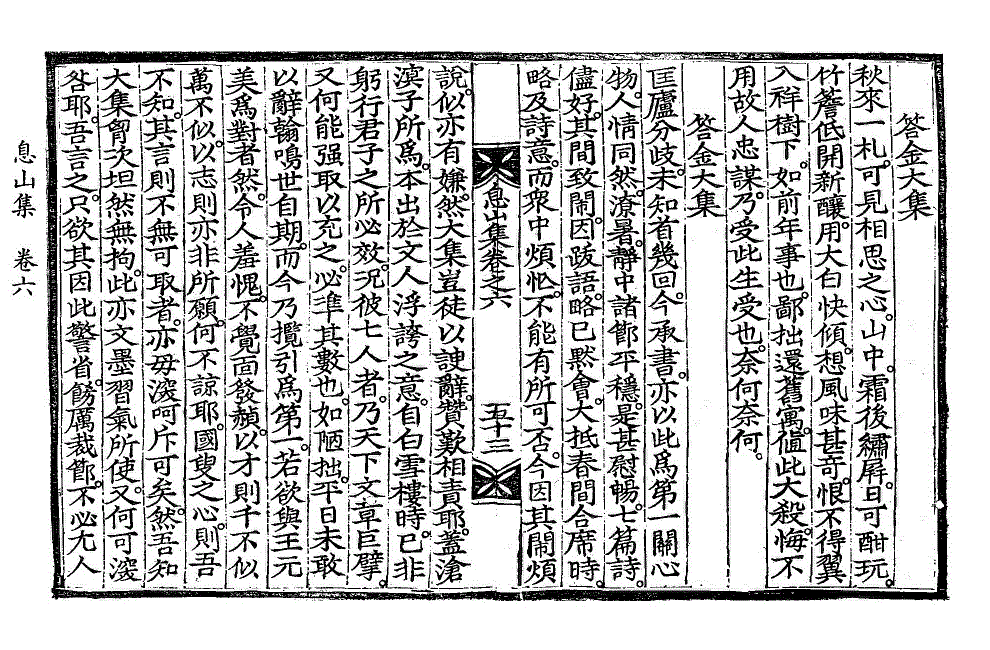 答金大集
答金大集匡庐分歧。未知首几回。今承书。亦以此为第一关心物。人情同然。潦暑。静中诸节平稳。是甚慰畅。七篇诗。尽好。其间致闹。因跋语。略已默会。大抵春间合席时。略及诗意。而众中烦忙。不能有所可否。今因其闹烦说。似亦有嫌。然大集岂徒以谀辞。赞叹相责耶。盖沧溟子所为。本出于文人浮誇之意。自白雪楼时。已非躬行君子之所必效。况彼七人者。乃天下文章巨擘。又何能强取以充之。必准其数也。如陋拙。平日未敢以辞翰鸣世自期。而今乃揽引为第一。若欲与王元美为对者然。令人羞愧。不觉面发赪。以才则千不似万不似。以志则亦非所愿。何不谅耶。国叟之心。则吾不知。其言则不无可取者。亦毋深呵斥可矣。然吾知大集胸次坦然无拘。此亦文墨习气所使。又何可深咎耶。吾言之。只欲其因此警省。饬厉裁节。不必尤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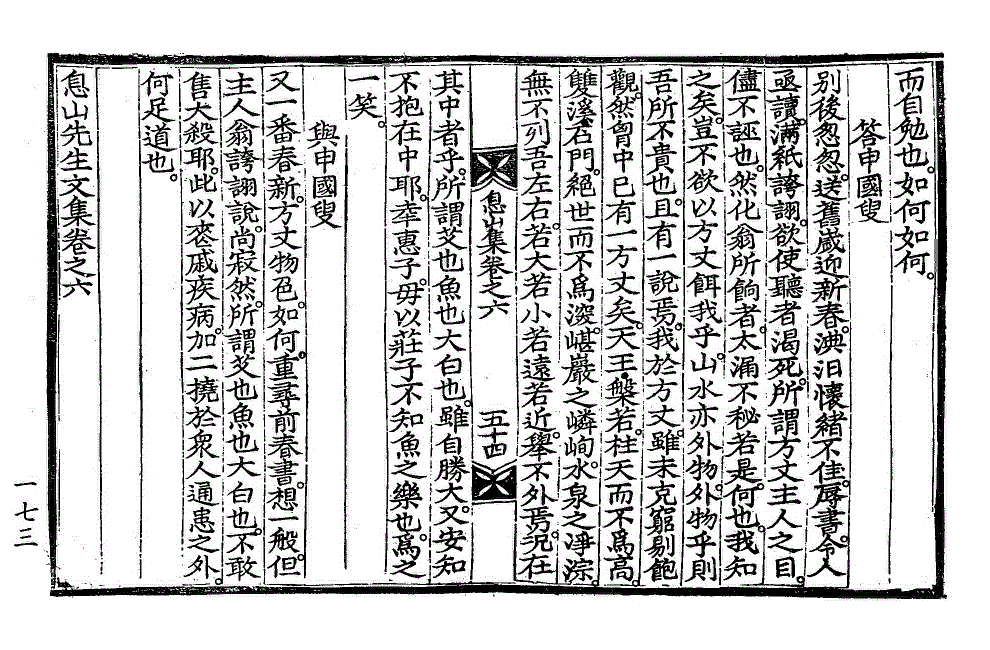 而自勉也。如何如何。
而自勉也。如何如何。答申国叟
别后匆匆。送旧岁迎新春。淟汩怀绪不佳。辱书。令人亟读。满纸誇诩。欲使听者渴死。所谓方丈主人之目。尽不诬也。然化翁所饷者。太漏不秘若是。何也。我知之矣。岂不欲以方丈饵我乎。山水亦外物。外物乎则吾所不贵也。且有一说焉。我于方丈。虽未克穷剔饱观。然胸中已有一方丈矣。天王,槃若。柱天而不为高。双溪,石门。绝世而不为深。嵁岩之嶙峋。水泉之净淙。无不列吾左右。若大若小若远若近。举不外焉。况在其中者乎。所谓艾也鱼也大白也。虽自胜大。又安知不抱在中耶。幸惠子。毋以庄子不知鱼之乐也。为之一笑。
与申国叟
又一番春新。方丈物色。如何。重寻前春书。想一般。但主人翁誇诩说。尚寂然。所谓艾也鱼也大白也。不敢售大杀耶。此以丧戚疾病。加二挠于众人通患之外。何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