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书
书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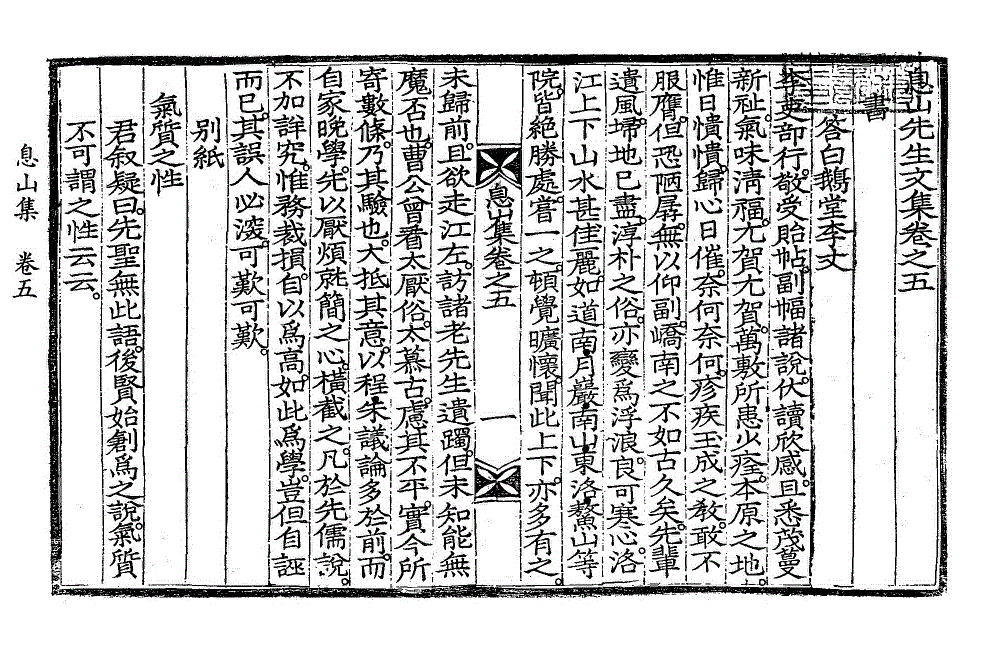 答白鹅堂李丈
答白鹅堂李丈李吏部行。敬受贻帖。副幅诸说。伏读欣感。且悉茂蔓新祉。气味清福。尤贺尤贺。万敷所患少痊。本原之地。惟日愦愦。归心日催。奈何奈何。疹疾玉成之教。敢不服膺。但恐陋孱。无以仰副。峤南之不如古久矣。先辈遗风。埽地已尽。淳朴之俗。亦变为浮浪。良可寒心。洛江上下山水甚佳丽。如道南,月岩,南山,东洛,鳌山等院。皆绝胜处。尝一之。顿觉旷怀。闻此上下。亦多有之。未归前。且欲走江左。访诸老先生遗躅。但未知能无魔否也。曹公曾看太厌俗。太慕古。虑其不平。实今所寄数条。乃其验也。大抵其意。以程,朱议论多于前。而自家晚学。先以厌烦就简之心。横截之。凡于先儒说。不加详究。惟务裁损。自以为高。如此为学。岂但自诬而已。其误人必深。可叹可叹。
别纸
气质之性
君叙疑曰。先圣无此语。后贤始创为之说。气质不可谓之性云云。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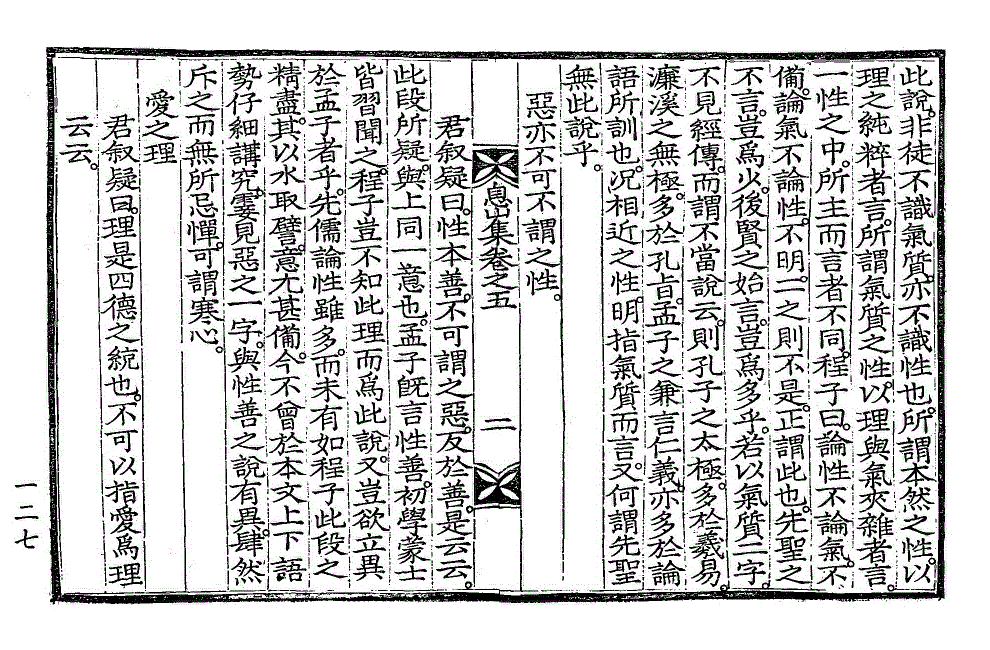 此说。非徒不识气质。亦不识性也。所谓本然之性。以理之纯粹者言。所谓气质之性。以理与气夹杂者言。一性之中。所主而言者不同。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正谓此也。先圣之不言。岂为少。后贤之始言。岂为多乎。若以气质二字。不见经传。而谓不当说云。则孔子之太极。多于羲易。濂溪之无极。多于孔旨。孟子之兼言仁义。亦多于论语所训也。况相近之性。明指气质而言。又何谓先圣无此说乎。
此说。非徒不识气质。亦不识性也。所谓本然之性。以理之纯粹者言。所谓气质之性。以理与气夹杂者言。一性之中。所主而言者不同。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正谓此也。先圣之不言。岂为少。后贤之始言。岂为多乎。若以气质二字。不见经传。而谓不当说云。则孔子之太极。多于羲易。濂溪之无极。多于孔旨。孟子之兼言仁义。亦多于论语所训也。况相近之性。明指气质而言。又何谓先圣无此说乎。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君叙疑曰。性本善。不可谓之恶。反于善。是云云。
此段所疑。与上同一意也。孟子既言性善。初学蒙士皆习闻之。程子岂不知此理而为此说。又岂欲立异于孟子者乎。先儒论性虽多。而未有如程子此段之精尽。其以水取譬。意尤甚备。今不曾于本文上下语势仔细讲究。霎见恶之一字。与性善之说有异。肆然斥之而无所忌惮。可谓寒心。
爱之理
君叙疑曰。理是四德之统也。不可以指爱为理云云。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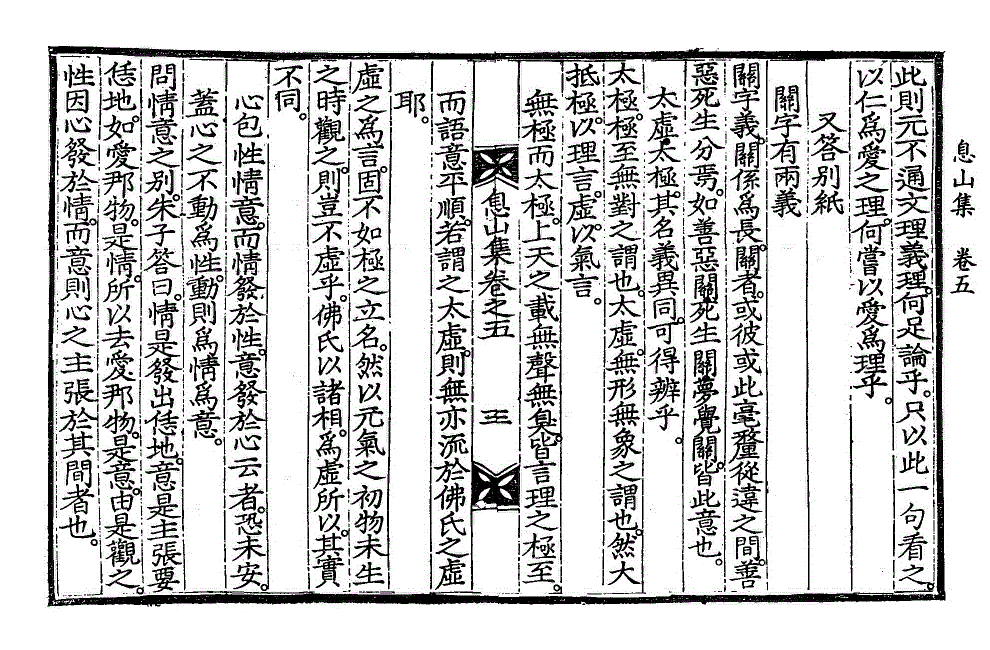 此则元不通文理义理。何足论乎。只以此一句看之。以仁为爱之理。何尝以爱为理乎。
此则元不通文理义理。何足论乎。只以此一句看之。以仁为爱之理。何尝以爱为理乎。又答别纸
关字有两义
关字义。关系为长。关者。或彼或此毫釐从违之间。善恶死生分焉。如善恶关,死生关,梦觉关。皆此意也。
太虚,太极。其名义异同。可得辨乎。
太极。极至无对之谓也。太虚。无形无象之谓也。然大抵极。以理言。虚。以气言。
无极而太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皆言理之极至。而语意平顺。若谓之太虚。则无亦流于佛氏之虚耶。
虚之为言。固不如极之立名。然以元气之初物未生之时观之。则岂不虚乎。佛氏以诸相。为虚所以。其实不同。
心包性情意。而情发于性。意发于心云者。恐未安。盖心之不动为性。动则为情为意。
问情意之别。朱子答曰。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由是观之。性因心发于情。而意则心之主张于其间者也。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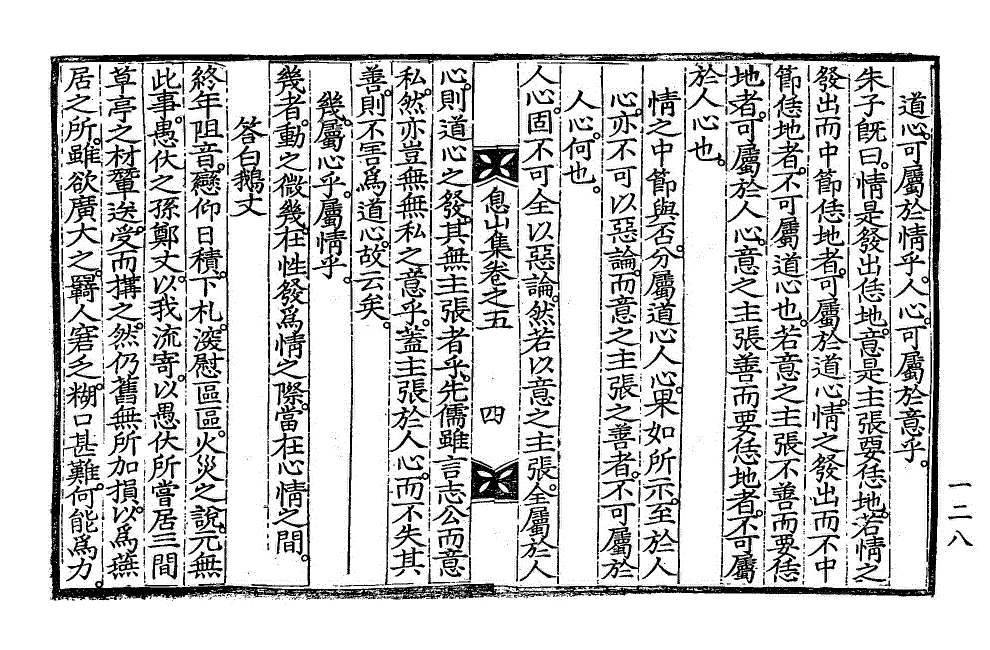 道心。可属于情乎。人心。可属于意乎。
道心。可属于情乎。人心。可属于意乎。朱子既曰。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若情之发出而中节恁地者。可属于道心。情之发出而不中节恁地者。不可属道心也。若意之主张不善而要恁地者。可属于人心。意之主张善而要恁地者。不可属于人心也。
情之中节与否。分属道心人心。果如所示。至于人心。亦不可以恶论。而意之主张之善者。不可属于人心。何也。
人心。固不可全以恶论。然若以意之主张。全属于人心。则道心之发。其无主张者乎。先儒虽言志公而意私。然亦岂无无私之意乎。盖主张于人心。而不失其善。则不害为道心。故云矣。
几。属心乎。属情乎。
几者。动之微几。在性发为情之际。当在心情之间。
答白鹅丈
终年阻音。恋仰日积。下札。深慰区区。火灾之说。元无此事。愚伏之孙郑丈。以我流寄。以愚伏所尝居三间草亭之材辇送。受而搆之。然仍旧无所加损。以为燕居之所。虽欲广大之。羁人窘乏。糊口甚难。何能为力。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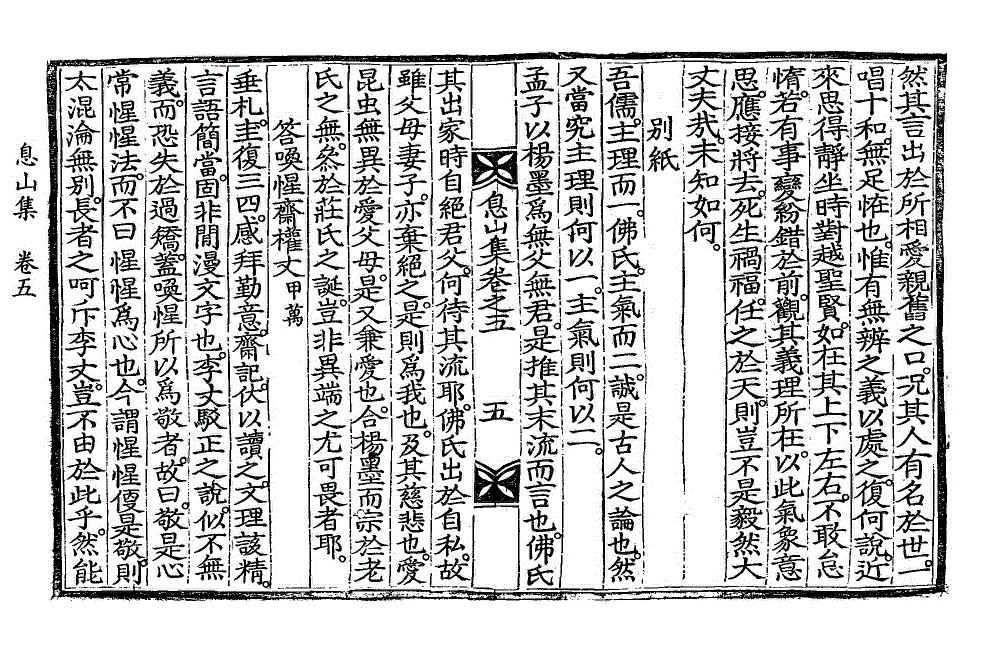 然其言出于所相爱亲旧之口。况其人有名于世。一唱十和。无足怪也。惟有无辨之义以处之。复何说。近来思得静坐时对越圣贤。如在其上下左右。不敢怠惰。若有事变纷错于前。观其义理所在。以此气象意思。应接将去。死生祸福。任之于天。则岂不是毅然大丈夫哉。未知如何。
然其言出于所相爱亲旧之口。况其人有名于世。一唱十和。无足怪也。惟有无辨之义以处之。复何说。近来思得静坐时对越圣贤。如在其上下左右。不敢怠惰。若有事变纷错于前。观其义理所在。以此气象意思。应接将去。死生祸福。任之于天。则岂不是毅然大丈夫哉。未知如何。别纸
吾儒。主理而一。佛氏。主气而二。诚是古人之论也。然又当究主理则何以一。主气则何以二。
孟子以杨墨为无父无君。是推其末流而言也。佛氏其出家时自绝君父。何待其流耶。佛氏出于自私。故虽父母妻子。亦弃绝之。是则为我也。及其慈悲也。爱昆虫无异于爱父母。是又兼爱也。合杨,墨而宗于老氏之无。参于庄氏之诞。岂非异端之尤可畏者耶。
答唤惺斋权丈(甲万)
垂札。圭复三四。感拜勤意。斋记。伏以读之。文理该精。言语简当。固非閒漫文字也。李丈驳正之说。似不无义。而恐失于过矫。盖唤惺所以为敬者。故曰。敬是心常惺惺法。而不曰惺惺为心也。今谓惺惺便是敬。则太混沦无别。长者之呵斥李丈。岂不由于此乎。然能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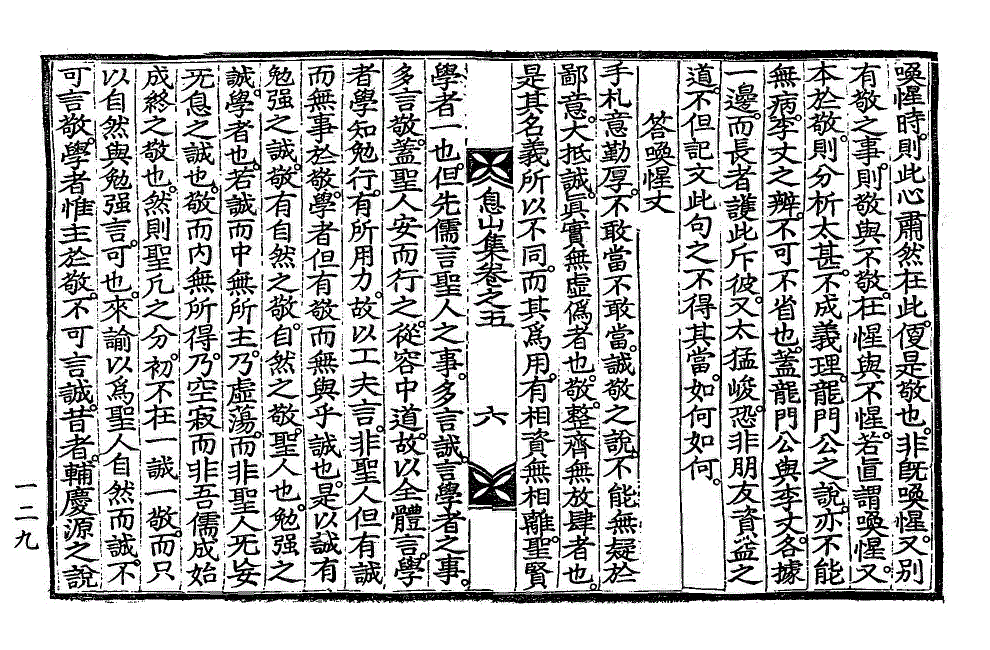 唤惺时。则此心肃然在此。便是敬也。非既唤惺。又别有敬之事。则敬与不敬。在惺与不惺。若直谓唤惺。又本于敬。则分析太甚。不成义理。龙门公之说。亦不能无病。李丈之辨。不可不省也。盖龙门公与李丈。各据一边。而长者护此斥彼。又太猛峻。恐非朋友资益之道。不但记文此句之不得其当。如何如何。
唤惺时。则此心肃然在此。便是敬也。非既唤惺。又别有敬之事。则敬与不敬。在惺与不惺。若直谓唤惺。又本于敬。则分析太甚。不成义理。龙门公之说。亦不能无病。李丈之辨。不可不省也。盖龙门公与李丈。各据一边。而长者护此斥彼。又太猛峻。恐非朋友资益之道。不但记文此句之不得其当。如何如何。答唤惺丈
手札意勤厚。不敢当不敢当。诚敬之说。不能无疑于鄙意。大抵诚。真实无虚伪者也。敬。整齐无放肆者也。是其名义所以不同。而其为用。有相资无相离。圣贤学者一也。但先儒言圣人之事。多言诚。言学者之事。多言敬。盖圣人安而行之。从容中道。故以全体言。学者学知勉行。有所用力。故以工夫言。非圣人但有诚而无事于敬。学者但有敬而无与乎诚也。是以诚有勉强之诚。敬有自然之敬。自然之敬。圣人也。勉强之诚。学者也。若诚而中无所主。乃虚荡。而非圣人无妄无息之诚也。敬而内无所得。乃空寂而非吾儒成始成终之敬也。然则圣凡之分。初不在一诚一敬。而只以自然与勉强言。可也。来谕以为圣人自然而诚。不可言敬。学者惟主于敬。不可言诚。昔者。辅庆源之说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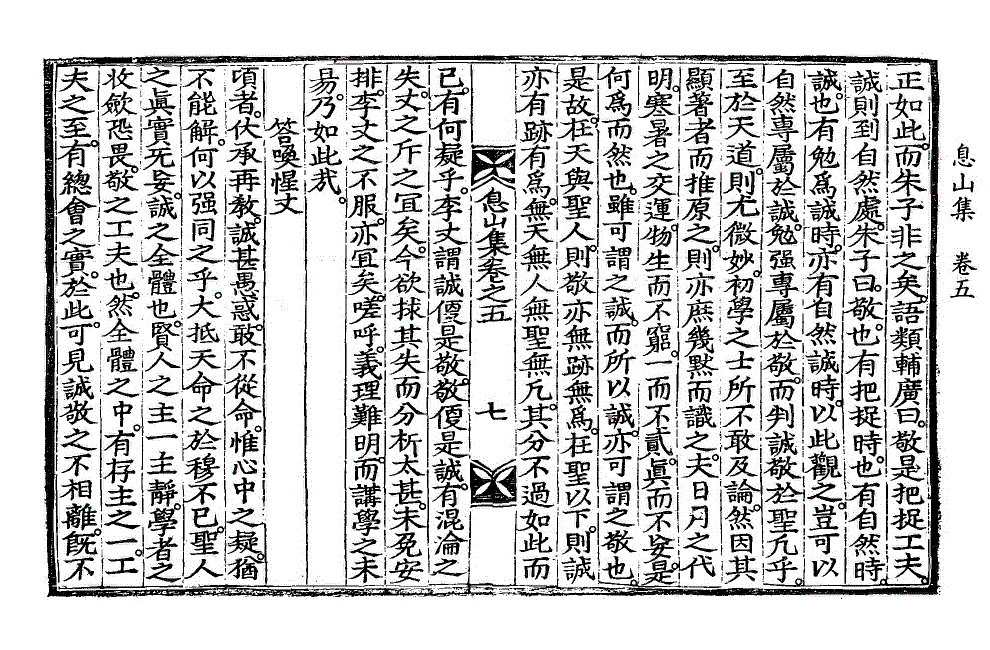 正如此。而朱子非之矣。语类辅广曰。敬是把捉工夫。诚则到自然处。朱子曰。敬。也有把捉时。也有自然时。诚。也有勉为诚时。亦有自然诚时。以此观之。岂可以自然专属于诚。勉强专属于敬。而判诚敬于圣凡乎。至于天道。则尤微妙。初学之士所不敢及论。然因其显著者而推原之。则亦庶几默而识之。夫日月之代明。寒暑之交运。物生而不穷。一而不贰。真而不妄。是何为而然也。虽可谓之诚。而所以诚。亦可谓之敬也。是故。在天与圣人。则敬亦无迹无为。在圣以下。则诚亦有迹有为。无天无人无圣无凡。其分不过如此而已。有何疑乎。李丈谓诚便是敬。敬便是诚。有混沦之失。丈之斥之宜矣。今欲救其失而分析太甚。未免安排。李丈之不服。亦宜矣。嗟呼。义理难明。而讲学之未易。乃如此哉。
正如此。而朱子非之矣。语类辅广曰。敬是把捉工夫。诚则到自然处。朱子曰。敬。也有把捉时。也有自然时。诚。也有勉为诚时。亦有自然诚时。以此观之。岂可以自然专属于诚。勉强专属于敬。而判诚敬于圣凡乎。至于天道。则尤微妙。初学之士所不敢及论。然因其显著者而推原之。则亦庶几默而识之。夫日月之代明。寒暑之交运。物生而不穷。一而不贰。真而不妄。是何为而然也。虽可谓之诚。而所以诚。亦可谓之敬也。是故。在天与圣人。则敬亦无迹无为。在圣以下。则诚亦有迹有为。无天无人无圣无凡。其分不过如此而已。有何疑乎。李丈谓诚便是敬。敬便是诚。有混沦之失。丈之斥之宜矣。今欲救其失而分析太甚。未免安排。李丈之不服。亦宜矣。嗟呼。义理难明。而讲学之未易。乃如此哉。答唤惺丈
顷者。伏承再教。诚甚愚惑。敢不从命。惟心中之疑。犹不能解。何以强同之乎。大抵天命之于穆不已。圣人之真实无妄。诚之全体也。贤人之主一主静。学者之收敛恐畏。敬之工夫也。然全体之中。有存主之一。工夫之至。有总会之实。于此。可见诚敬之不相离。既不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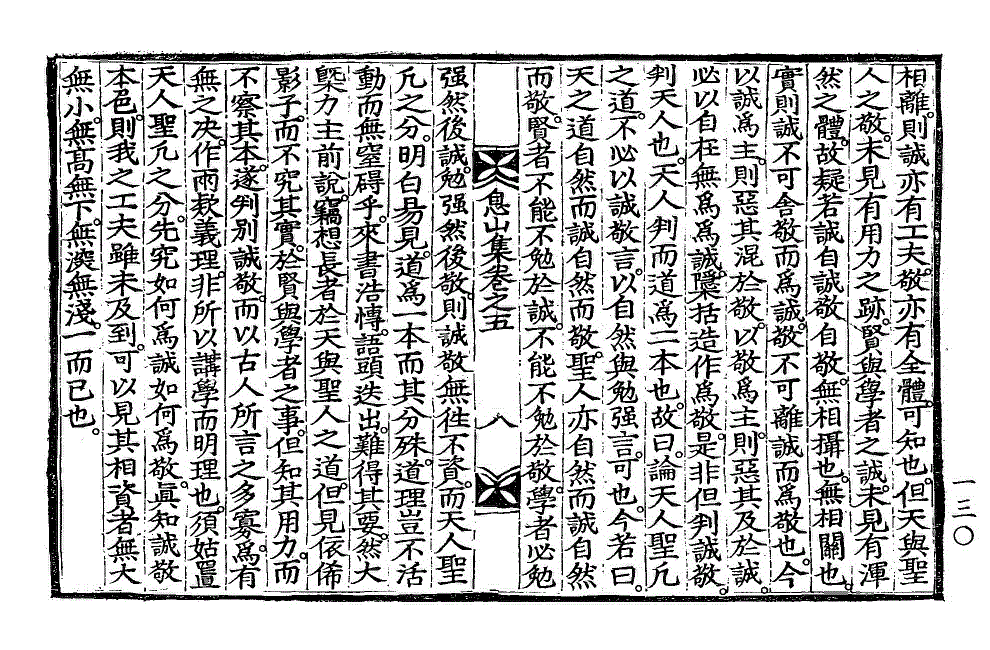 相离。则诚亦有工夫。敬亦有全体。可知也。但天与圣人之敬。未见有用力之迹。贤与学者之诚。未见有浑然之体。故疑若诚自诚敬自敬。无相摄也。无相关也。实则诚不可舍敬而为诚。敬不可离诚而为敬也。今以诚为主。则恶其混于敬。以敬为主。则恶其及于诚。必以自在无为为诚。檃括造作为敬。是非但判诚敬。判天人也。天人判而道为二本也。故曰。论天人圣凡之道。不必以诚敬言。以自然与勉强言。可也。今若曰。天之道自然而诚自然而敬。圣人亦自然而诚自然而敬。贤者不能不勉于诚。不能不勉于敬。学者必勉强然后诚。勉强然后敬。则诚敬无往不资。而天人圣凡之分。明白易见。道为一本而其分殊。道理岂不活动而无窒碍乎。来书浩博。语头迭出。难得其要。然大槩力主前说。窃想长者于天与圣人之道。但见依俙影子。而不究其实。于贤与学者之事。但知其用力。而不察其本。遂判别诚敬。而以古人所言之多寡。为有无之决。作两款义理。非所以讲学而明理也。须姑置天人圣凡之分。先究如何为诚如何为敬。真知诚敬本色。则我之工夫虽未及到。可以见其相资者无大无小。无高无下。无深无浅。一而已也。
相离。则诚亦有工夫。敬亦有全体。可知也。但天与圣人之敬。未见有用力之迹。贤与学者之诚。未见有浑然之体。故疑若诚自诚敬自敬。无相摄也。无相关也。实则诚不可舍敬而为诚。敬不可离诚而为敬也。今以诚为主。则恶其混于敬。以敬为主。则恶其及于诚。必以自在无为为诚。檃括造作为敬。是非但判诚敬。判天人也。天人判而道为二本也。故曰。论天人圣凡之道。不必以诚敬言。以自然与勉强言。可也。今若曰。天之道自然而诚自然而敬。圣人亦自然而诚自然而敬。贤者不能不勉于诚。不能不勉于敬。学者必勉强然后诚。勉强然后敬。则诚敬无往不资。而天人圣凡之分。明白易见。道为一本而其分殊。道理岂不活动而无窒碍乎。来书浩博。语头迭出。难得其要。然大槩力主前说。窃想长者于天与圣人之道。但见依俙影子。而不究其实。于贤与学者之事。但知其用力。而不察其本。遂判别诚敬。而以古人所言之多寡。为有无之决。作两款义理。非所以讲学而明理也。须姑置天人圣凡之分。先究如何为诚如何为敬。真知诚敬本色。则我之工夫虽未及到。可以见其相资者无大无小。无高无下。无深无浅。一而已也。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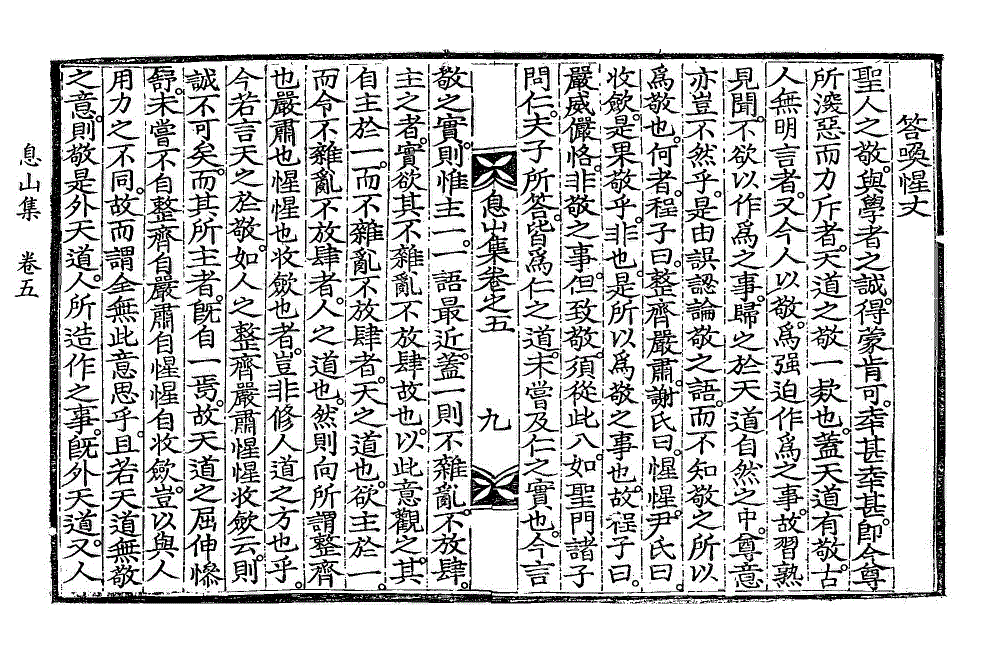 答唤惺丈
答唤惺丈圣人之敬。与学者之诚。得蒙肯可。幸甚幸甚。即今尊所深恶而力斥者。天道之敬一款也。盖天道有敬。古人无明言者。又今人以敬。为强迫作为之事。故习熟见闻。不欲以作为之事。归之于天道自然之中。尊意亦岂不然乎。是由误认论敬之语。而不知敬之所以为敬也。何者。程子曰。整齐严肃。谢氏曰。惺惺。尹氏曰。收敛。是果敬乎。非也。是所以为敬之事也。故程子曰。严威俨恪。非敬之事。但致敬。须从此入。如圣门诸子问仁。夫子所答。皆为仁之道。未尝及仁之实也。今言敬之实。则惟主一。一语最近。盖一则不杂乱。不放肆。主之者。实欲其不杂乱不放肆故也。以此意观之。其自主于一。而不杂乱不放肆者。天之道也。欲主于一。而令不杂乱不放肆者。人之道也。然则向所谓整齐也严肃也惺惺也收敛也者。岂非修人道之方也乎。今若言天之于敬。如人之整齐严肃惺惺收敛云。则诚不可矣。而其所主者。既自一焉。故天道之屈伸惨舒。未尝不自整齐自严肃自惺惺自收敛。岂以与人用力之不同。故而谓全无此意思乎。且若天道无敬之意。则敬是外天道。人所造作之事。既外天道。又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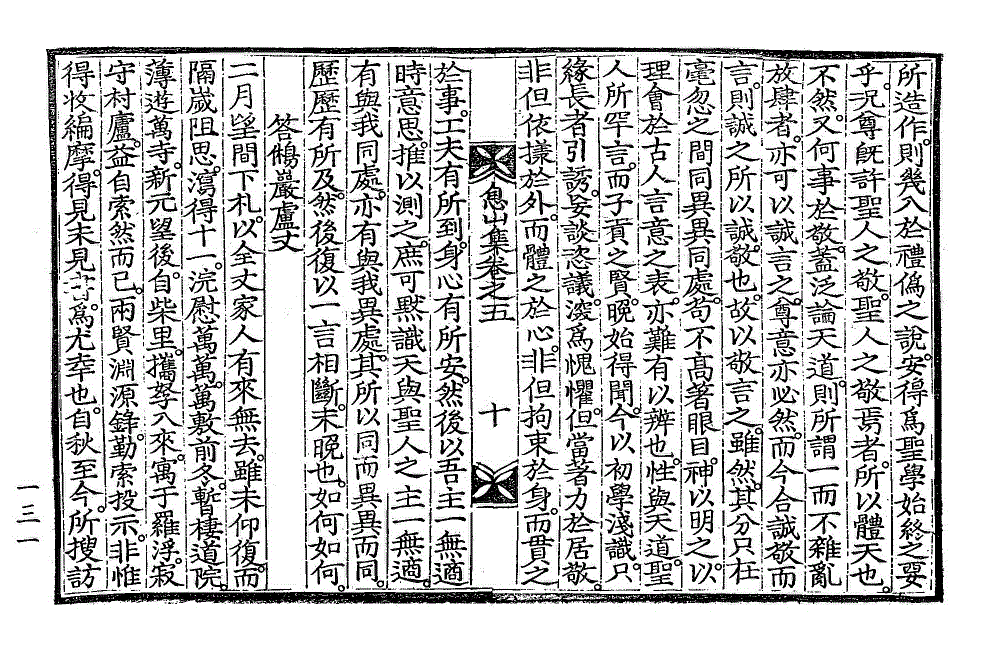 所造作。则几入于礼伪之说。安得为圣学始终之要乎。况尊既许圣人之敬。圣人之敬焉者。所以体天也。不然。又何事于敬。盖泛论天道。则所谓一而不杂乱放肆者。亦可以诚言之。尊意亦必然。而今合诚敬而言。则诚之所以诚。敬也。故以敬言之。虽然。其分只在毫忽之间同异异同处。苟不高著眼目。神以明之。以理会于古人言意之表。亦难有以辨也。性与天道。圣人所罕言。而子贡之贤。晚始得闻。今以初学浅识。只缘长者引诱。妄谈恣议。深为愧惧。但当著力于居敬。非但依㨾于外。而体之于心。非但拘束于身。而贯之于事。工夫有所到。身心有所安。然后以吾主一无适时意思。推以测之。庶可默识天与圣人之主一无适。有与我同处。亦有与我异处。其所以同而异异而同。历历有所及。然后复以一言相断。未晚也。如何如何。
所造作。则几入于礼伪之说。安得为圣学始终之要乎。况尊既许圣人之敬。圣人之敬焉者。所以体天也。不然。又何事于敬。盖泛论天道。则所谓一而不杂乱放肆者。亦可以诚言之。尊意亦必然。而今合诚敬而言。则诚之所以诚。敬也。故以敬言之。虽然。其分只在毫忽之间同异异同处。苟不高著眼目。神以明之。以理会于古人言意之表。亦难有以辨也。性与天道。圣人所罕言。而子贡之贤。晚始得闻。今以初学浅识。只缘长者引诱。妄谈恣议。深为愧惧。但当著力于居敬。非但依㨾于外。而体之于心。非但拘束于身。而贯之于事。工夫有所到。身心有所安。然后以吾主一无适时意思。推以测之。庶可默识天与圣人之主一无适。有与我同处。亦有与我异处。其所以同而异异而同。历历有所及。然后复以一言相断。未晚也。如何如何。答鸺岩卢丈
二月望间下札。以全丈家人有来无去。虽未仰复。而隔岁阻思。泻得十一。浣慰万万。万敷前冬。暂栖道院。薄游万寺。新元望后。自柴里。携孥入来。寓于罗浮。寂守村庐。益自索然而已。两贤渊源录。勤索投示。非惟得收编摩。得见未见书。为尤幸也。自秋至今。所搜访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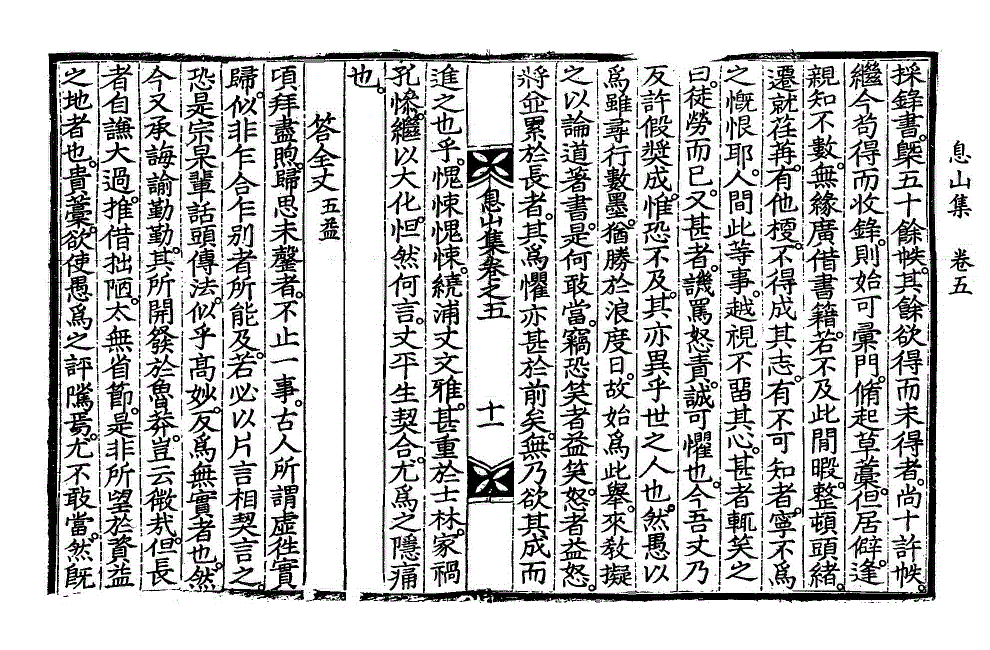 采录书。槩五十馀帙。其馀欲得而未得者。尚十许帙。继今苟得而收录。则始可汇门。脩起草藁。但居僻。逢亲知不数。无缘广借书籍。若不及此閒暇。整顿头绪。迁就荏苒。有他梗。不得成其志。有不可知者。宁不为之慨恨耶。人间此等事。越视不留其心。甚者辄笑之曰。徒劳而已。又甚者。讥骂怒责。诚可惧也。今吾丈乃反许假奖成。惟恐不及。其亦异乎世之人也。然愚以为虽寻行数墨。犹胜于浪度日。故始为此举。来教拟之以论道著书。是何敢当。窃恐笑者益笑。怒者益怒。将并累于长者。其为惧亦甚于前矣。无乃欲其成而进之也乎。愧悚愧悚。绕浦丈文雅。甚重于士林。家祸孔惨。继以大化。怛然何言。丈平生契合。尤为之隐痛也。
采录书。槩五十馀帙。其馀欲得而未得者。尚十许帙。继今苟得而收录。则始可汇门。脩起草藁。但居僻。逢亲知不数。无缘广借书籍。若不及此閒暇。整顿头绪。迁就荏苒。有他梗。不得成其志。有不可知者。宁不为之慨恨耶。人间此等事。越视不留其心。甚者辄笑之曰。徒劳而已。又甚者。讥骂怒责。诚可惧也。今吾丈乃反许假奖成。惟恐不及。其亦异乎世之人也。然愚以为虽寻行数墨。犹胜于浪度日。故始为此举。来教拟之以论道著书。是何敢当。窃恐笑者益笑。怒者益怒。将并累于长者。其为惧亦甚于前矣。无乃欲其成而进之也乎。愧悚愧悚。绕浦丈文雅。甚重于士林。家祸孔惨。继以大化。怛然何言。丈平生契合。尤为之隐痛也。答全丈(五益)
顷拜尽煦。归思未罄者。不止一事。古人所谓虚往实归。似非乍合乍别者所能及。若必以片言相契言之。恐是宗杲辈话头传法。似乎高妙。反为无实者也。然今又承诲谕勤勤。其所开发于鲁莽。岂云微哉。但长者自谦大过。推借拙陋。太无省节。是非所望于资益之地者也。贵藁。欲使愚为之评骘焉。尤不敢当。然既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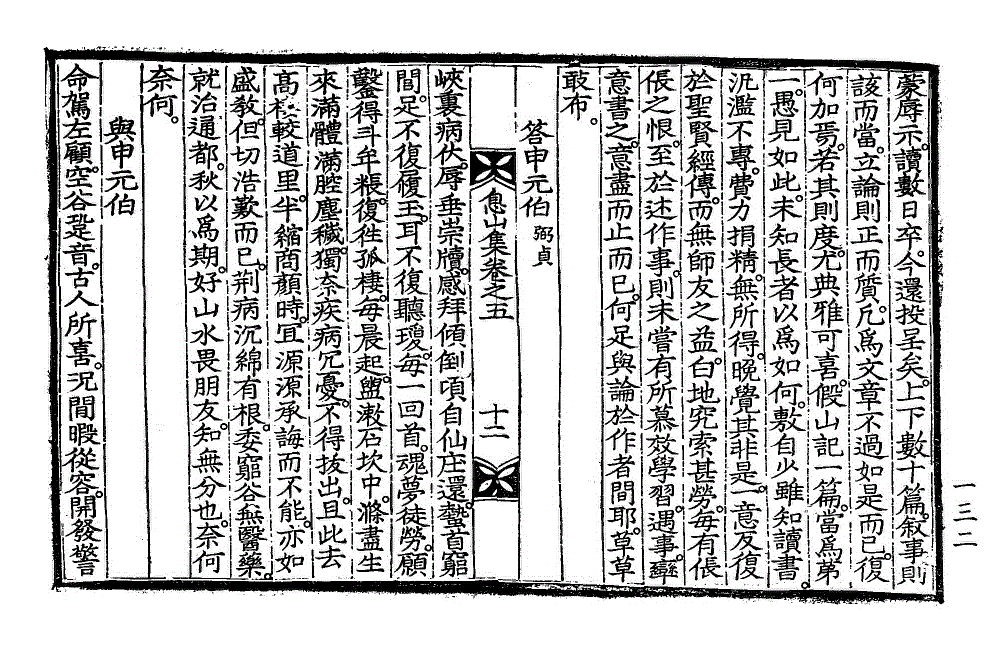 蒙辱示。读数日卒。今还投呈矣。上下数十篇。叙事则该而当。立论则正而质。凡为文章不过如是而已。复何加焉。若其则度。尤典雅可喜。假山记一篇。当为第一。愚见如此。未知长者以为如何。敷自少虽知读书。汎滥不专。费力捐精。无所得。晚觉其非是。一意反复于圣贤经传。而无师友之益。白地究索甚劳。每有伥伥之恨。至于述作事。则未尝有所慕效学习。遇事。率意书之。意尽而止而已。何足与论于作者间耶。草草敢布。
蒙辱示。读数日卒。今还投呈矣。上下数十篇。叙事则该而当。立论则正而质。凡为文章不过如是而已。复何加焉。若其则度。尤典雅可喜。假山记一篇。当为第一。愚见如此。未知长者以为如何。敷自少虽知读书。汎滥不专。费力捐精。无所得。晚觉其非是。一意反复于圣贤经传。而无师友之益。白地究索甚劳。每有伥伥之恨。至于述作事。则未尝有所慕效学习。遇事。率意书之。意尽而止而已。何足与论于作者间耶。草草敢布。答申元伯(弼贞)
峡里病伏。辱垂崇牍。感拜倾倒。顷自仙庄还。蛰首穷闾。足不复履玉。耳不复听琼。每一回首。魂梦徒劳。愿凿得斗牟粻。复往孤栖。每晨起。盥漱石坎中。涤尽生来满体满腔尘秽。独奈疾病冗忧。不得拔出。且此去高栖较道里。半缩商颜时。宜源源承诲而不能。亦如盛教。但切浩叹而已。荆病沉绵有根。委穷谷无医药。就治通都。秋以为期。好山水畏朋友。知无分也。奈何奈何。
与申元伯
命驾左顾。空谷跫音。古人所喜。况閒暇从容。开发警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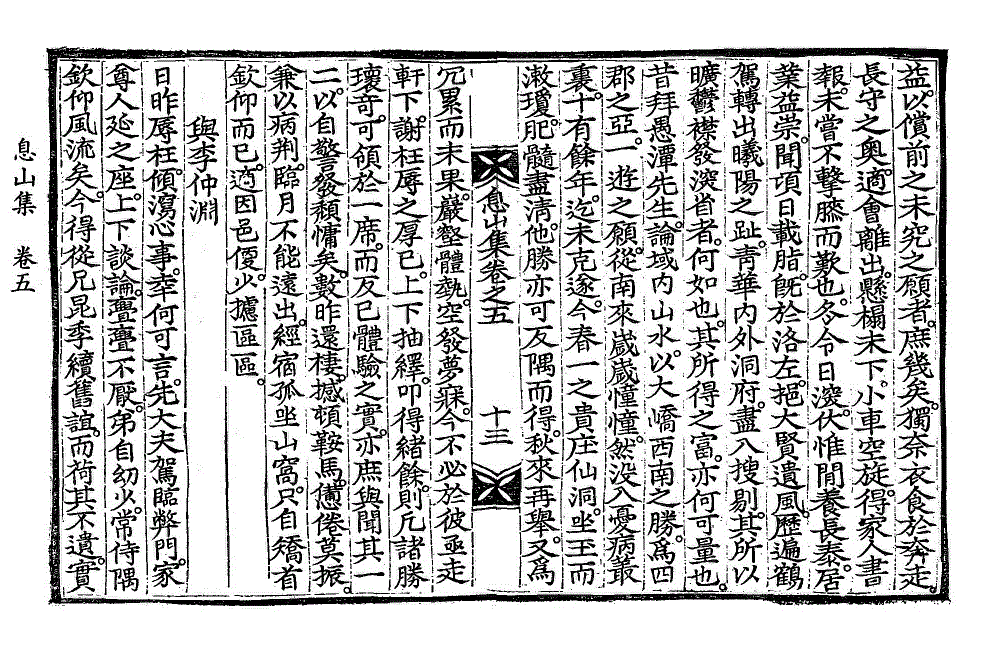 益。以偿前之未究之愿者。庶几矣。独奈衣食于奔走。长守之奥。适会离出。悬榻未下。小车空旋。得家人书报。未尝不击膝而叹也。冬令日深。伏惟閒养长泰。居业益崇。闻顷日载脂。既于洛左。挹大贤遗风。历遍鹤驾转出曦阳之趾。青华内外洞府。尽入搜剔。其所以旷郁襟发深省者。何如也。其所得之富。亦何可量也。昔拜愚潭先生。论域内山水。以大峤西南之胜。为四郡之亚。一游之愿。从南来岁岁憧憧。然没入忧病丛里。十有馀年。迄未克遂。今春一之贵庄仙洞。坐玉而漱琼。肌髓尽清。他胜亦可反隅而得。秋来再举。又为冗累而未果。岩壑体势。空发梦寐。今不必于彼亟走轩下。谢枉辱之厚已。上下抽绎。叩得绪馀。则凡诸胜瑰奇。可领于一席。而反已体验之实。亦庶与闻其一二。以自警发颓慵矣。数昨还栖。撼顿鞍马。惫倦莫振。兼以病荆。临月不能远出。经宿孤坐山窝。只自矫首钦仰而已。适因邑便。少摅区区。
益。以偿前之未究之愿者。庶几矣。独奈衣食于奔走。长守之奥。适会离出。悬榻未下。小车空旋。得家人书报。未尝不击膝而叹也。冬令日深。伏惟閒养长泰。居业益崇。闻顷日载脂。既于洛左。挹大贤遗风。历遍鹤驾转出曦阳之趾。青华内外洞府。尽入搜剔。其所以旷郁襟发深省者。何如也。其所得之富。亦何可量也。昔拜愚潭先生。论域内山水。以大峤西南之胜。为四郡之亚。一游之愿。从南来岁岁憧憧。然没入忧病丛里。十有馀年。迄未克遂。今春一之贵庄仙洞。坐玉而漱琼。肌髓尽清。他胜亦可反隅而得。秋来再举。又为冗累而未果。岩壑体势。空发梦寐。今不必于彼亟走轩下。谢枉辱之厚已。上下抽绎。叩得绪馀。则凡诸胜瑰奇。可领于一席。而反已体验之实。亦庶与闻其一二。以自警发颓慵矣。数昨还栖。撼顿鞍马。惫倦莫振。兼以病荆。临月不能远出。经宿孤坐山窝。只自矫首钦仰而已。适因邑便。少摅区区。与李仲渊
日昨辱枉。倾泻心事。幸何可言。先大夫驾临弊门。家尊人延之座。上下谈论。亹亹不厌。弟自幼少。常侍隅钦仰风流矣。今得从兄昆季续旧谊。而荷其不遗。实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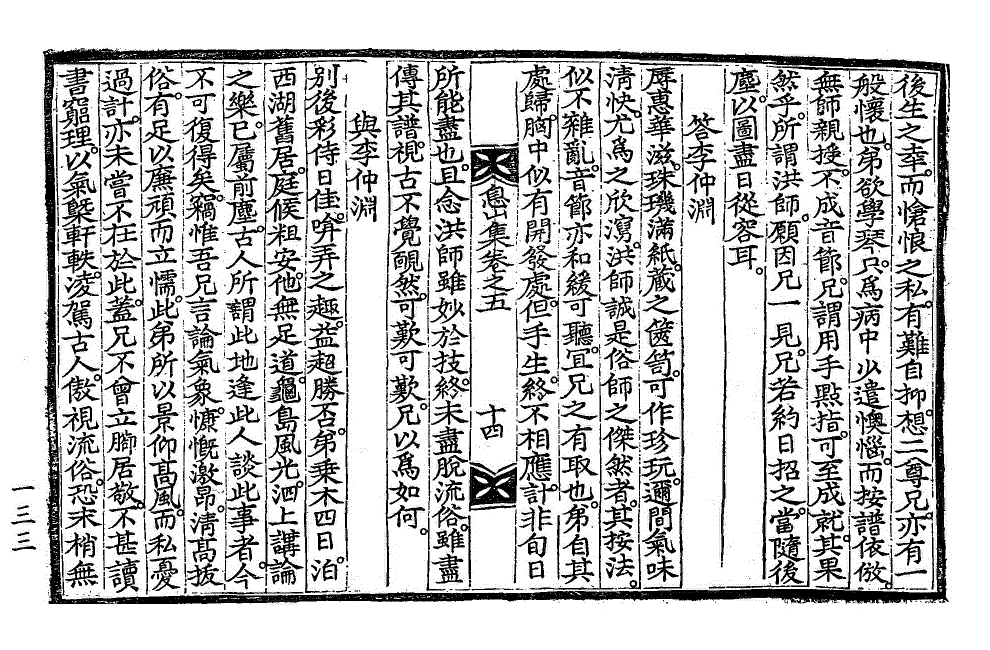 后生之幸。而怆悢之私。有难自抑。想二尊兄。亦有一般怀也。弟欲学琴。只为病中少遣懊恼。而按谱依仿。无师亲授。不成音节。兄谓用手点指。可至成就。其果然乎。所谓洪师。愿因兄一见。兄若约日招之。当随后尘。以图尽日从容耳。
后生之幸。而怆悢之私。有难自抑。想二尊兄。亦有一般怀也。弟欲学琴。只为病中少遣懊恼。而按谱依仿。无师亲授。不成音节。兄谓用手点指。可至成就。其果然乎。所谓洪师。愿因兄一见。兄若约日招之。当随后尘。以图尽日从容耳。答李仲渊
辱惠华滋。珠玑满纸。藏之箧笥。可作珍玩。迩间气味清快。尤为之欣泻。洪师诚是俗师之杰然者。其按法。似不杂乱。音节亦和缓可听。宜兄之有取也。弟自其处归。胸中似有开发处。但手生。终不相应。计非旬日所能尽也。且念洪师虽妙于技。终未尽脱流俗。虽尽传其谱。视古不觉腼然。可叹可叹。兄以为如何。
与李仲渊
别后彩侍日佳。啽弄之趣。益超胜否。弟乘木四日。泊西湖旧居。庭候粗安。他无足道。龟岛风光。泗上讲论之乐。已属前尘。古人所谓此地逢此人谈此事者。今不可复得矣。窃惟吾兄言论气象。慷慨激昂。清高拔俗。有足以廉顽而立懦。此弟所以景仰高风。而私忧过计。亦未尝不在于此。盖兄不曾立脚居敬。不甚读书穷理。以气槩轩轶。凌驾古人。傲视流俗。恐末梢无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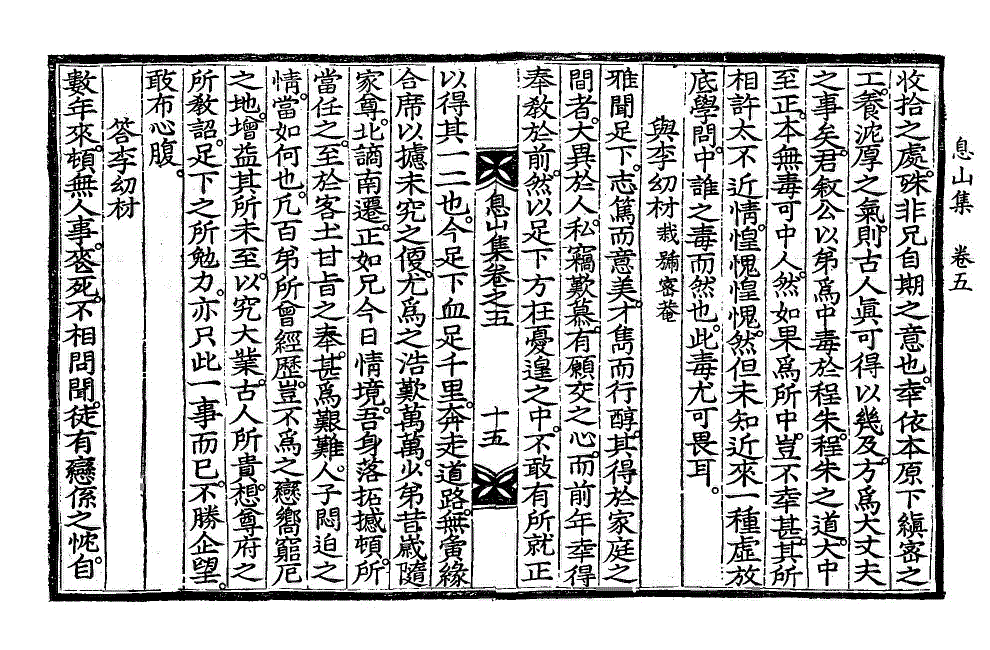 收拾之处。殊非兄自期之意也。幸依本原下缜密之工。养沈厚之气。则古人真可得以几及。方为大丈夫之事矣。君叙公以弟为中毒于程朱。程朱之道。大中至正。本无毒可中人。然如果为所中。岂不幸甚。其所相许太不近情。惶愧惶愧。然但未知近来一种虚放底学问。中谁之毒而然也。此毒尤可畏耳。
收拾之处。殊非兄自期之意也。幸依本原下缜密之工。养沈厚之气。则古人真可得以几及。方为大丈夫之事矣。君叙公以弟为中毒于程朱。程朱之道。大中至正。本无毒可中人。然如果为所中。岂不幸甚。其所相许太不近情。惶愧惶愧。然但未知近来一种虚放底学问。中谁之毒而然也。此毒尤可畏耳。与李幼材(栽号密庵)
雅闻足下。志笃而意美。才隽而行醇。其得于家庭之间者。大异于人。私窃叹慕。有愿交之心。而前年幸得奉教于前。然以足下方在忧遑之中。不敢有所就正以得其一二也。今足下血足千里。奔走道路。无夤缘合席以摅未究之便。尤为之浩叹万万。少弟昔岁随家尊。北谪南迁。正如兄今日情境。吾身落拓撼顿。所当任之。至于客土甘旨之奉。甚为艰难。人子闷迫之情。当如何也。凡百弟所曾经历。岂不为之恋向穷厄之地。增益其所未至。以究大业。古人所贵。想尊府之所教诏。足下之所勉力。亦只此一事而已。不胜企望。敢布心腹。
答李幼材
数年来。顿无人事。丧死。不相问闻。徒有恋系之忱。自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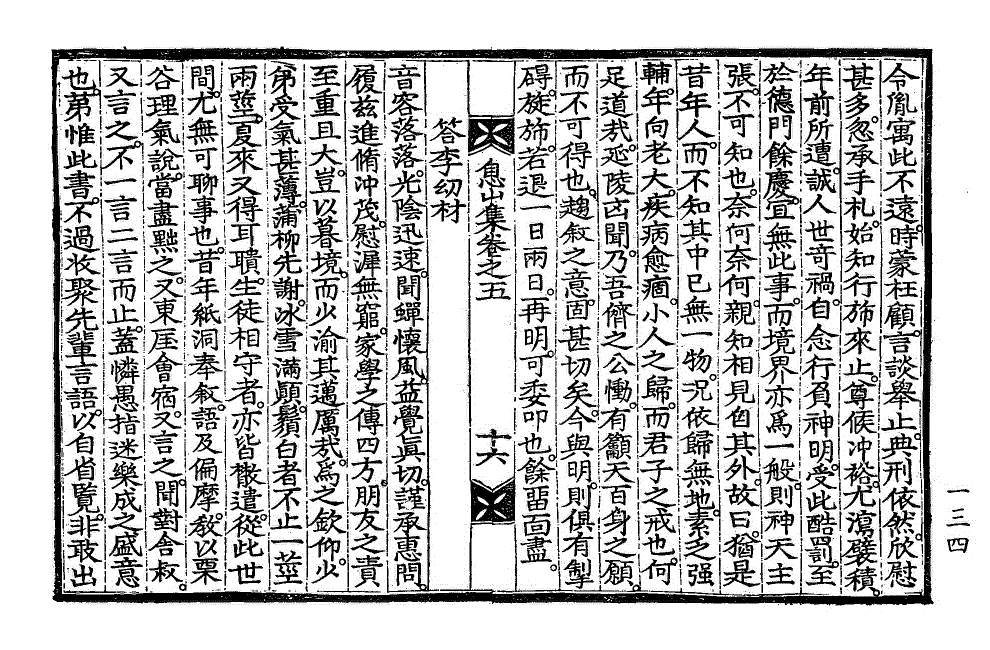 令胤寓此不远。时蒙枉顾。言谈举止。典刑依然。欣慰甚多。忽承手札。始知行旆来止。尊候冲裕。尤泻襞积。年前所遭。诚人世奇祸。自念行负神明。受此酷罚。至于德门馀庆。宜无此事。而境界亦为一般。则神天主张。不可知也。奈何奈何。亲知相见自其外。故曰。犹是昔年人。而不知其中已无一物。况依归无地。素乏强辅。年向老大。疾病愈痼。小人之归。而君子之戒也。何足道哉。延陵凶闻。乃吾侪之公恸。有吁天百身之愿。而不可得也。趋叙之意。固甚切矣。今与明。则俱有掣碍。旋旆。若退一日两日。再明。可委叩也。馀留面尽。
令胤寓此不远。时蒙枉顾。言谈举止。典刑依然。欣慰甚多。忽承手札。始知行旆来止。尊候冲裕。尤泻襞积。年前所遭。诚人世奇祸。自念行负神明。受此酷罚。至于德门馀庆。宜无此事。而境界亦为一般。则神天主张。不可知也。奈何奈何。亲知相见自其外。故曰。犹是昔年人。而不知其中已无一物。况依归无地。素乏强辅。年向老大。疾病愈痼。小人之归。而君子之戒也。何足道哉。延陵凶闻。乃吾侪之公恸。有吁天百身之愿。而不可得也。趋叙之意。固甚切矣。今与明。则俱有掣碍。旋旆。若退一日两日。再明。可委叩也。馀留面尽。答李幼材
音容落落。光阴迅速。闻蝉怀风。益觉真切。谨承惠问。履玆进脩冲茂。慰漽无穷。家学之传四方。朋友之责至重且大。岂以暮境。而少渝其迈厉哉。为之钦仰。少弟受气甚薄。蒲柳先谢。冰雪满颠。须白者不止一茎两茎。夏来又得耳聩。生徒相守者。亦皆散遣。从此世间。尤无可聊事也。昔年纸洞奉叙。语及偏摩。教以栗谷理气说。当尽黜之。又东厓会宿。又言之。闻对舍叔。又言之。不一言二言而止。盖怜愚指迷乐成之盛意也。第惟此书。不过收聚先辈言语。以自省览。非敢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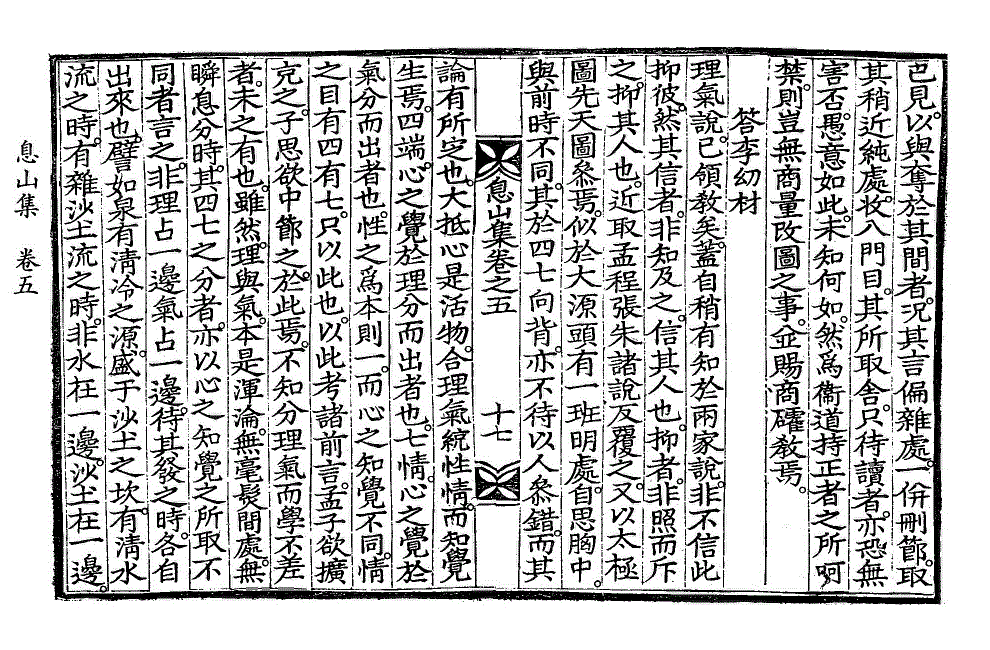 己见。以与夺于其间者。况其言偏杂处。一并删节。取其稍近纯处。收入门目。其所取舍。只待读者。亦恐无害否。愚意如此。未知何如。然为卫道持正者之所呵禁。则岂无商量改图之事。并赐商礭教焉。
己见。以与夺于其间者。况其言偏杂处。一并删节。取其稍近纯处。收入门目。其所取舍。只待读者。亦恐无害否。愚意如此。未知何如。然为卫道持正者之所呵禁。则岂无商量改图之事。并赐商礭教焉。答李幼材
理气说。已领教矣。盖自稍有知于两家说。非不信此抑彼。然其信者。非知及之。信其人也。抑者。非照而斥之。抑其人也。近取孟程张朱诸说反覆之。又以太极图先天图参焉。似于大源头有一班明处。自思胸中。与前时不同。其于四七向背。亦不待以人参错。而其论有所定也。大抵心是活物。合理气统性情。而知觉生焉。四端。心之觉于理分而出者也。七情。心之觉于气分而出者也。性之为本则一。而心之知觉不同。情之目有四有七。只以此也。以此考诸前言。孟子欲扩充之。子思欲中节之。于此焉。不知分理气而学不差者。未之有也。虽然。理与气。本是浑沦。无毫发间处。无瞬息分时。其四七之分者。亦以心之知觉之所取不同者言之。非理占一边气占一边。待其发之时。各自出来也。譬如泉有清冷之源。盛于沙土之坎。有清水流之时。有杂沙土流之时。非水在一边。沙土在一边。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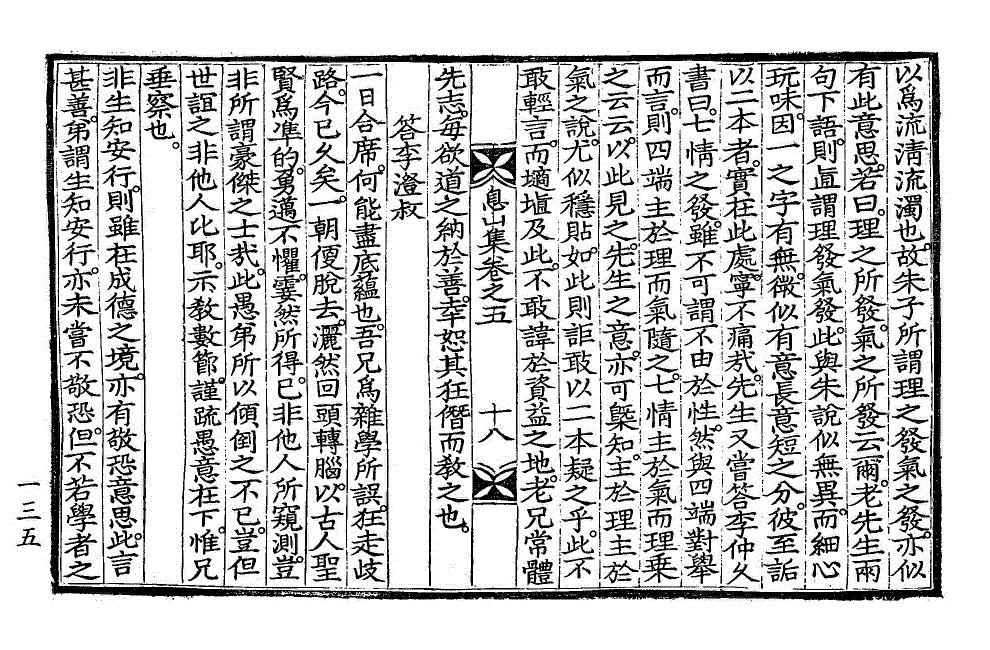 以为流清流浊也。故朱子所谓理之发气之发。亦似有此意思。若曰。理之所发。气之所发云尔。老先生两句下语。则直谓理发气发。此与朱说似无异。而细心玩味。因一之字有无。微似有意长意短之分。彼至诟以二本者。实在此处。宁不痛哉。先生又尝答李仲久书曰。七情之发。虽不可谓不由于性。然与四端对举而言。则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云云。以此见之。先生之意。亦可槩知。主于理主于气之说。尤似稳贴。如此则讵敢以二本疑之乎。此不敢轻言。而擿埴及此。不敢讳于资益之地。老兄常体先志。每欲道之纳于善。幸恕其狂僭而教之也。
以为流清流浊也。故朱子所谓理之发气之发。亦似有此意思。若曰。理之所发。气之所发云尔。老先生两句下语。则直谓理发气发。此与朱说似无异。而细心玩味。因一之字有无。微似有意长意短之分。彼至诟以二本者。实在此处。宁不痛哉。先生又尝答李仲久书曰。七情之发。虽不可谓不由于性。然与四端对举而言。则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云云。以此见之。先生之意。亦可槩知。主于理主于气之说。尤似稳贴。如此则讵敢以二本疑之乎。此不敢轻言。而擿埴及此。不敢讳于资益之地。老兄常体先志。每欲道之纳于善。幸恕其狂僭而教之也。答李澄叔
一日合席。何能尽底蕴也。吾兄为杂学所误。狂走歧路。今已久矣。一朝便脱去。洒然回头转脑。以古人圣贤为准的。勇迈不惧。霎然所得。已非他人所窥测。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哉。此愚弟所以倾倒之不已。岂但世谊之非他人比耶。示教数节。谨疏愚意在下。惟兄垂察也。
非生知安行。则虽在成德之境。亦有敬恐意思。此言甚善。弟谓生知安行。亦未尝不敬恐。但不若学者之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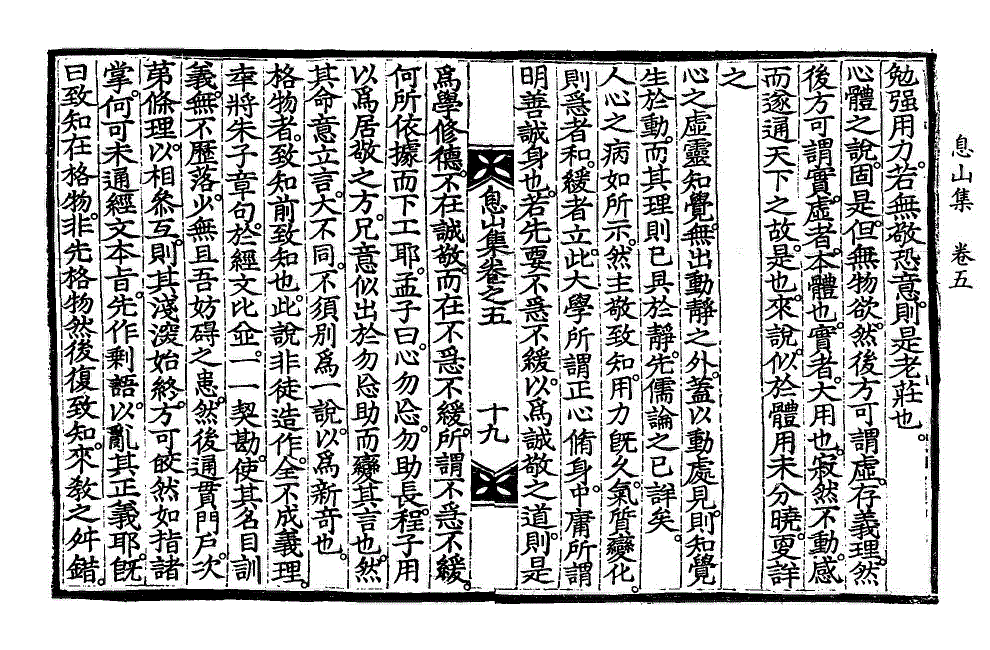 勉强用力。若无敬恐意。则是老庄也。
勉强用力。若无敬恐意。则是老庄也。心体之说。固是。但无物欲。然后方可谓虚。存义理。然后方可谓实。虚者。本体也。实者。大用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来说。似于体用未分晓。更详之。
心之虚灵知觉。无出动静之外。盖以动处见。则知觉生于动。而其理则已具于静。先儒论之已详矣。
人心之病如所示。然主敬致知。用力既久。气质变化。则急者和。缓者立。此大学所谓正心脩身。中庸所谓明善诚身也。若先要不急不缓。以为诚敬之道。则是为学修德。不在诚敬。而在不急不缓。所谓不急不缓。何所依据而下工耶。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程子用以为居敬之方。兄意似出于勿忘助而变其言也。然其命意立言。大不同。不须别为一说。以为新奇也。
格物者。致知前致知也。此说非徒造作。全不成义理。幸将朱子章句。于经文比并。一一契勘。使其名目训义。无不历落。少无且吾妨碍之患。然后通贯门户。次第条理。以相参互。则其浅深始终。方可皎然如指诸掌。何可未通经文本旨。先作剩语。以乱其正义耶。既曰致知在格物。非先格物然后复致知。来教之舛错。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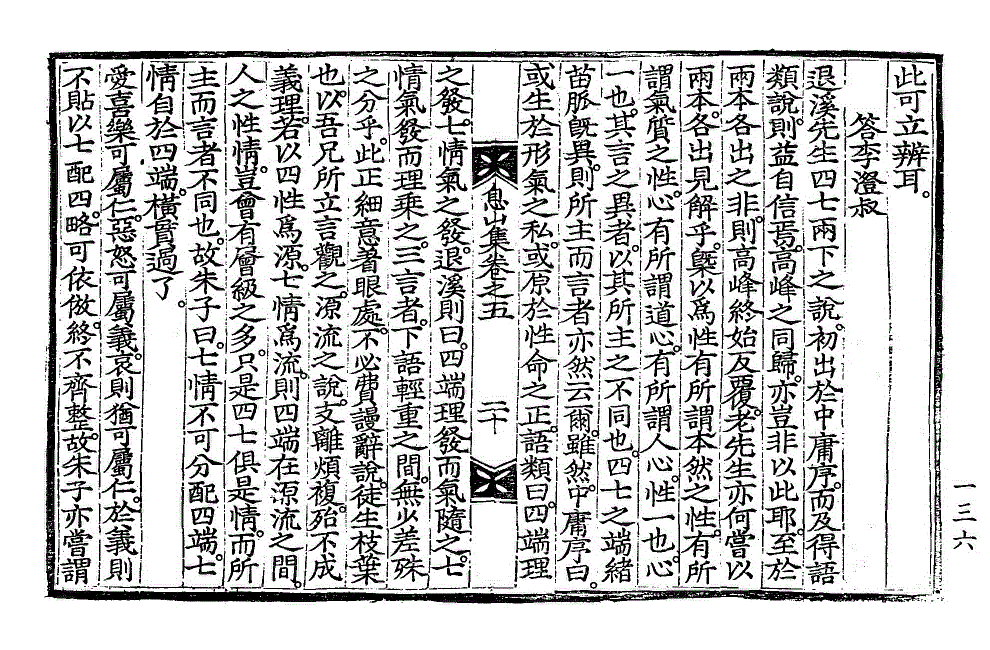 此可立辨耳。
此可立辨耳。答李澄叔
退溪先生四七两下之说。初出于中庸序。而及得语类说。则益自信焉。高峰之同归。亦岂非以此耶。至于两本各出之非。则高峰终始反覆。老先生亦何尝以两本。各出见解乎。槩以为性有所谓本然之性。有所谓气质之性。心有所谓道心。有所谓人心。性一也。心一也。其言之异者。以其所主之不同也。四七之端绪苗脉既异。则所主而言者亦然云尔。虽然。中庸序曰。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语类曰。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退溪则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三言者。下语轻重之间。无少差殊之分乎。此正细意着眼处。不必费谩辞说。徒生枝叶也。以吾兄所立言观之。源流之说。支离烦复。殆不成义理。若以四性为源。七情为流。则四端在源流之间。人之性情。岂曾有层级之多。只是四七俱是情。而所主而言者不同也。故朱子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
爱喜乐可属仁。恶怒可属义。哀则犹可属仁。于义则不贴以七配四。略可依仿。终不齐整。故朱子亦尝谓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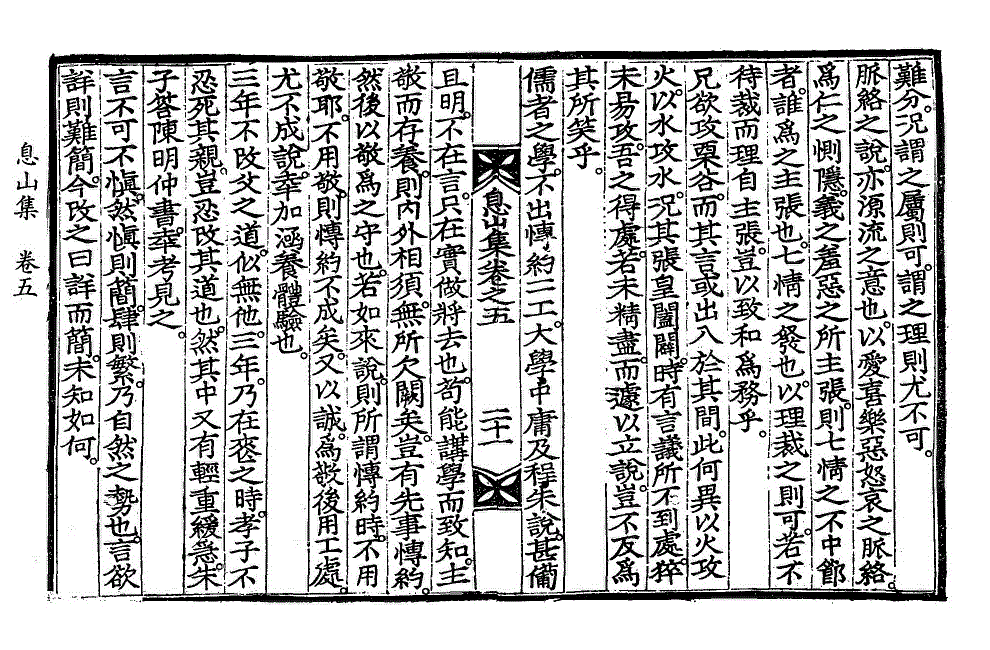 难分。况谓之属则可。谓之理则尤不可。
难分。况谓之属则可。谓之理则尤不可。脉络之说。亦源流之意也。以爱喜乐恶怒哀之脉络。为仁之恻隐。义之羞恶之所主张。则七情之不中节者。谁为之主张也。七情之发也。以理裁之则可。若不待裁而理自主张。岂以致和为务乎。
兄欲攻栗谷。而其言或出入于其间。此何异以火攻火。以水攻水。况其张皇阖辟。时有言议所不到处。猝未易攻。吾之得处。若未精尽。而遽以立说。岂不反为其所笑乎。
儒者之学。不出博约二工。大学,中庸及程,朱说。甚备且明。不在言。只在实做将去也。苟能讲学而致知。主敬而存养。则内外相须。无所欠阙矣。岂有先事博约。然后以敬为之守也。若如来说。则所谓博约时。不用敬耶。不用敬。则博约不成矣。又以诚。为敬后用工处。尤不成说。幸加涵养体验也。
三年不改父之道。似无他。三年。乃在丧之时。孝子不忍死其亲。岂忍改其道也。然其中又有轻重缓急。朱子答陈明仲书。幸考见之。
言不可不慎。然慎则简。肆则繁。乃自然之势也。言欲详则难简。今改之曰详而简。未知如何。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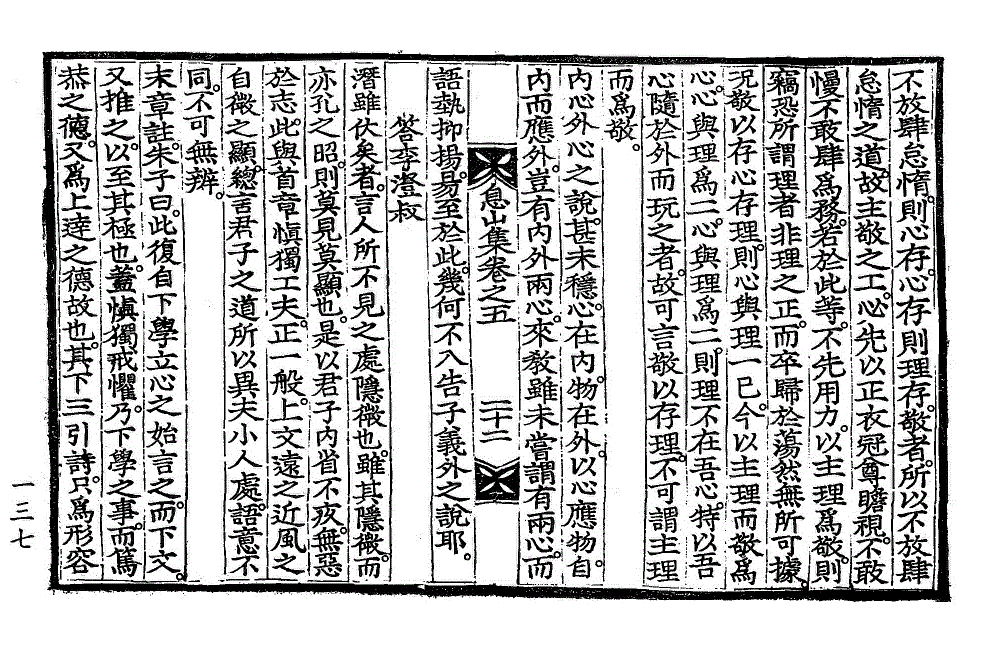 不放肆怠惰。则心存。心存则理存。敬者。所以不放肆怠惰之道。故主敬之工。必先以正衣冠尊瞻视。不敢慢不敢肆为务。若于此等。不先用力。以主理为敬。则窃恐所谓理者非理之正。而卒归于荡然无所可据。况敬以存心存理。则心与理一已。今以主理而敬为心。心与理为二。心与理为二。则理不在吾心。特以吾心随于外而玩之者。故可言敬以存理。不可谓主理而为敬。
不放肆怠惰。则心存。心存则理存。敬者。所以不放肆怠惰之道。故主敬之工。必先以正衣冠尊瞻视。不敢慢不敢肆为务。若于此等。不先用力。以主理为敬。则窃恐所谓理者非理之正。而卒归于荡然无所可据。况敬以存心存理。则心与理一已。今以主理而敬为心。心与理为二。心与理为二。则理不在吾心。特以吾心随于外而玩之者。故可言敬以存理。不可谓主理而为敬。内心外心之说。甚未稳。心在内。物在外。以心应物。自内而应外。岂有内外两心。来教虽未尝谓有两心。而语势抑扬。易至于此。几何不入告子义外之说耶。
答李澄叔
潜虽伏矣者。言人所不见之处隐微也。虽其隐微。而亦孔之昭。则莫见莫显也。是以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此与首章慎独工夫。正一般。上文远之近风之自微之显。总言君子之道所以异夫小人处。语意不同。不可无辨。
末章注。朱子曰。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盖慎独戒惧。乃下学之事。而笃恭之德。又为上达之德故也。其下三引诗。只为形容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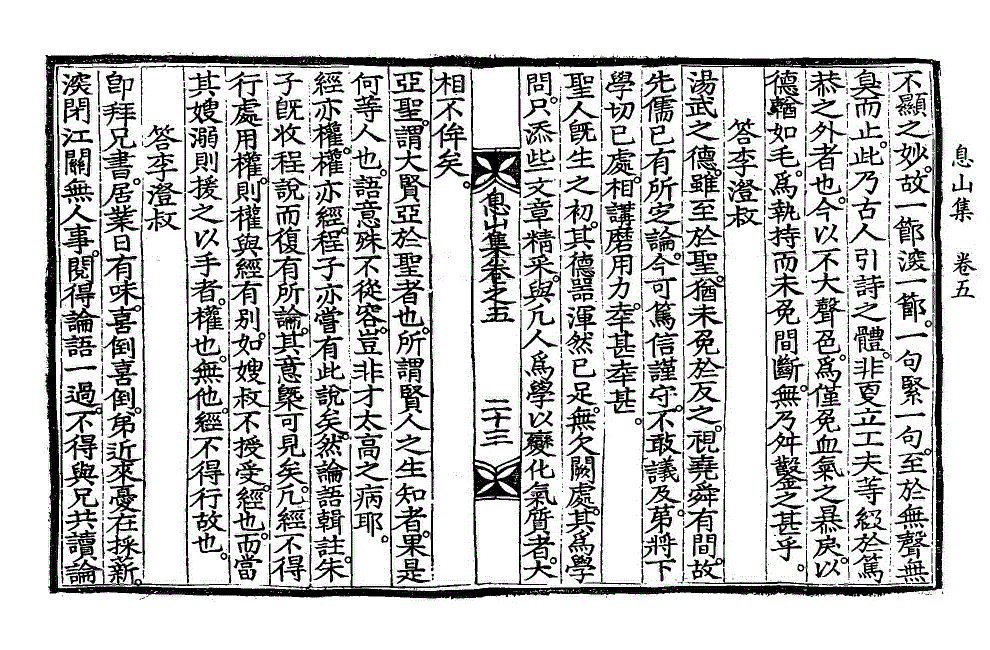 不显之妙。故一节深一节。一句紧一句。至于无声无臭而止。此乃古人引诗之体。非更立工夫等级于笃恭之外者也。今以不大声色。为仅免血气之暴戾。以德輶如毛。为执持而未免间断。无乃舛凿之甚乎。
不显之妙。故一节深一节。一句紧一句。至于无声无臭而止。此乃古人引诗之体。非更立工夫等级于笃恭之外者也。今以不大声色。为仅免血气之暴戾。以德輶如毛。为执持而未免间断。无乃舛凿之甚乎。答李澄叔
汤武之德。虽至于圣。犹未免于反之。视尧舜有间。故先儒已有所定论。今可笃信谨守。不敢议及。第将下学切己处。相讲磨用力。幸甚幸甚。
圣人既生之初。其德器浑然已足。无欠阙处。其为学问。只添些文章精采。与凡人为学以变化气质者。大相不侔矣。
亚圣。谓大贤亚于圣者也。所谓贤人之生知者。果是何等人也。语意殊不从容。岂非才太高之病耶。
经亦权。权亦经。程子亦尝有此说矣。然论语辑注。朱子既收程说而复有所论。其意槩可见矣。凡经不得行处用权。则权与经有别。如嫂叔不授受。经也。而当其嫂溺则援之以手者。权也。无他。经不得行故也。
答李澄叔
即拜兄书。居业日有味。喜倒喜倒。弟近来忧在采薪。深闭江关无人事。阅得论语一过。不得与兄共读论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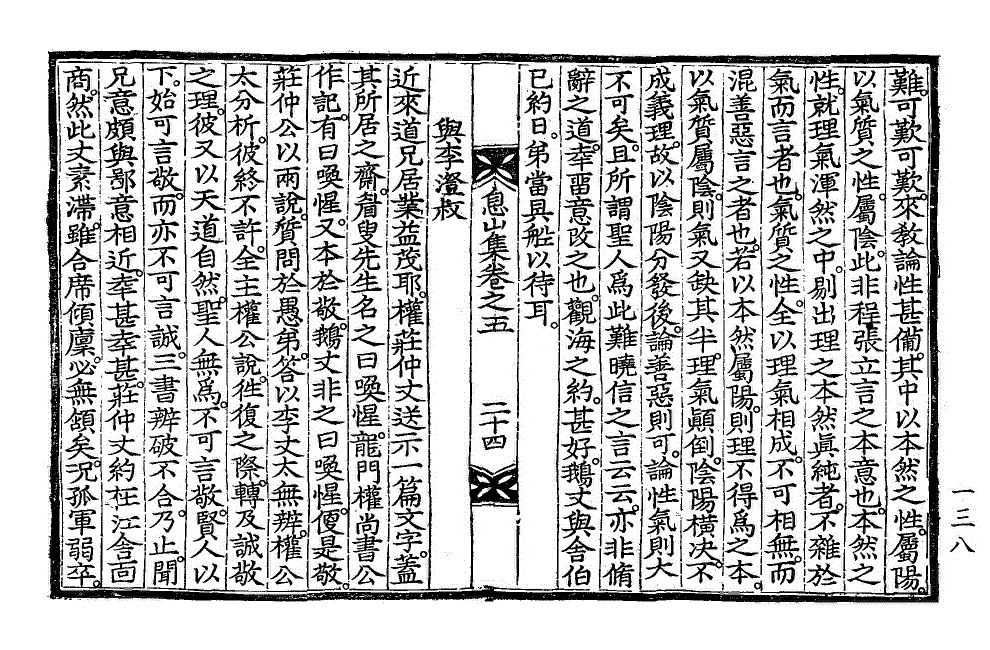 难。可叹可叹。来教论性甚备。其中以本然之性。属阳。以气质之性。属阴。此非程,张立言之本意也。本然之性。就理气浑然之中。剔出理之本然真纯者。不杂于气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全以理气相成。不可相无。而混善恶言之者也。若以本然属阳。则理不得为之本。以气质属阴。则气又缺其半。理气颠倒。阴阳横决。不成义理。故以阴阳分发后。论善恶则可。论性气则大不可矣。且所谓圣人为此难晓信之言云云。亦非脩辞之道。幸留意改之也。观海之约。甚好。鹅丈与舍伯已约日。弟当具船以待耳。
难。可叹可叹。来教论性甚备。其中以本然之性。属阳。以气质之性。属阴。此非程,张立言之本意也。本然之性。就理气浑然之中。剔出理之本然真纯者。不杂于气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全以理气相成。不可相无。而混善恶言之者也。若以本然属阳。则理不得为之本。以气质属阴。则气又缺其半。理气颠倒。阴阳横决。不成义理。故以阴阳分发后。论善恶则可。论性气则大不可矣。且所谓圣人为此难晓信之言云云。亦非脩辞之道。幸留意改之也。观海之约。甚好。鹅丈与舍伯已约日。弟当具船以待耳。与李澄叔
近来道兄居业益茂耶。权庄仲丈送示一篇文字。盖其所居之斋。眉叟先生名之曰唤惺。龙门权尚书公作记。有曰唤惺。又本于敬。鹅丈非之曰唤惺。便是敬。庄仲公以两说。质问于愚弟。答以李丈太无辨。权公太分析。彼终不许。全主权公说。往复之际。转及诚敬之理。彼又以天道自然。圣人无为。不可言敬。贤人以下。始可言敬。而亦不可言诚。三书辨破不合。乃止。闻兄意颇与鄙意相近。幸甚幸甚。庄仲丈约枉江舍面商。然此丈素滞。虽合席倾廪。必无颔矣。况孤军弱卒。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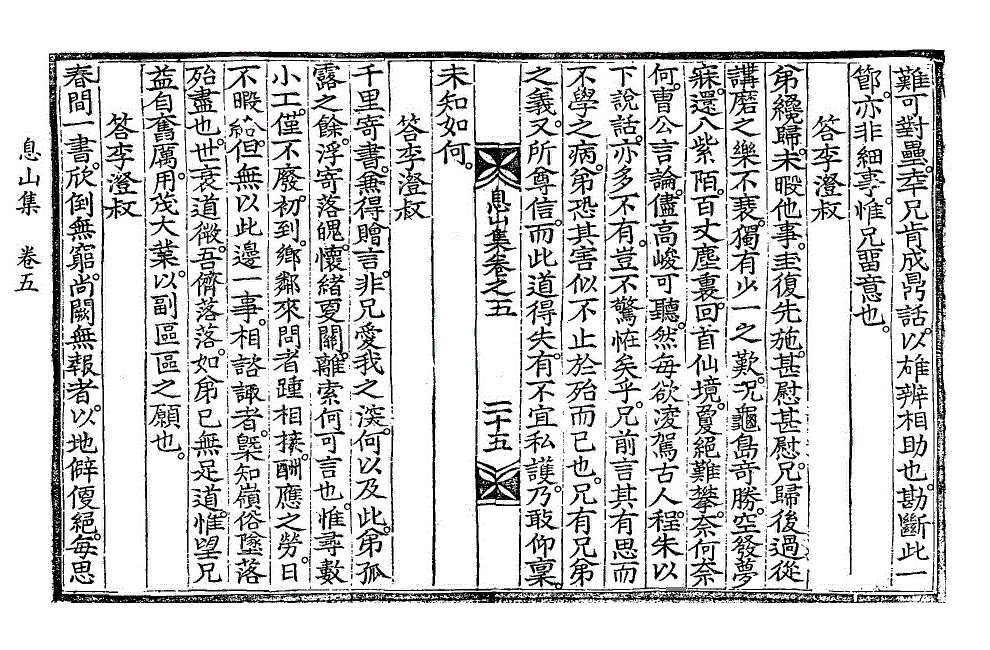 难可对垒。幸兄肯成鼎话。以雄辨相助也。勘断此一节。亦非细事。惟兄留意也。
难可对垒。幸兄肯成鼎话。以雄辨相助也。勘断此一节。亦非细事。惟兄留意也。答李澄叔
弟才归。未暇他事。圭复先施。甚慰甚慰。兄归后过从讲磨之乐不衰。独有少一之叹。况龟岛奇胜。空发梦寐。还入紫陌。百丈尘里。回首仙境。夐绝难攀。奈何奈何。曹公言论。尽高峻可听。然每欲凌驾古人。程朱以下说话。亦多不有。岂不惊怪矣乎。兄前言其有思而不学之病。弟恐其害似不止于殆而已也。兄有兄弟之义。又所尊信。而此道得失。有不宜私护。乃敢仰禀。未知如何。
答李澄叔
千里寄书。兼得赠言。非兄爱我之深。何以及此。弟孤露之馀。浮寄落魄。怀绪更关。离索何可言也。惟寻数小工。仅不废。初到。乡邻来问者踵相接。酬应之劳。日不暇给。但无以此边一事。相咨诹者。槩知岭俗坠落殆尽也。世衰道微。吾侪落落。如弟已无足道。惟望兄益自奋厉。用茂大业。以副区区之愿也。
答李澄叔
春间一书。欣倒无穷。尚阙无报者。以地僻便绝。每思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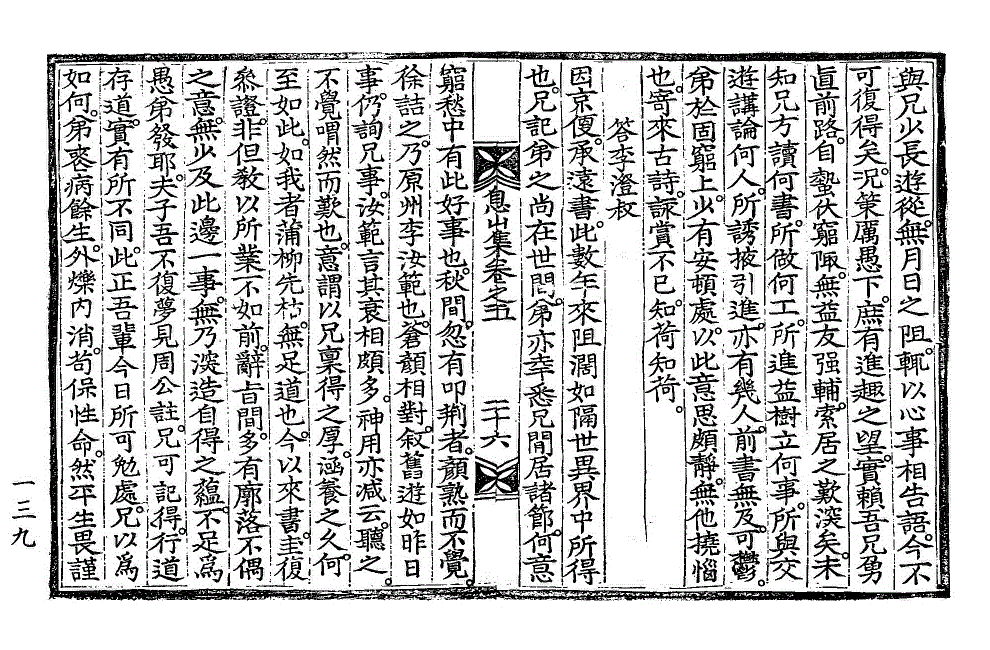 与兄少长游从。无月日之阻。辄以心事相告语。今不可复得矣。况策厉愚下。庶有进趣之望。实赖吾兄勇直前路。自蛰伏穷陬。无益友强辅。索居之叹深矣。未知兄方读何书。所做何工。所进益树立何事。所与交游讲论何人。所诱掖引进。亦有几人。前书无及。可郁。弟于固穷上。少有安顿处。以此意思颇静。无他挠恼也。寄来古诗。咏赏不已。知荷知荷。
与兄少长游从。无月日之阻。辄以心事相告语。今不可复得矣。况策厉愚下。庶有进趣之望。实赖吾兄勇直前路。自蛰伏穷陬。无益友强辅。索居之叹深矣。未知兄方读何书。所做何工。所进益树立何事。所与交游讲论何人。所诱掖引进。亦有几人。前书无及。可郁。弟于固穷上。少有安顿处。以此意思颇静。无他挠恼也。寄来古诗。咏赏不已。知荷知荷。答李澄叔
因京便。承远书。此数年来阻阔如隔世异界中所得也。兄记弟之尚在世间。弟亦幸悉兄閒居诸节。何意穷愁中有此好事也。秋间。忽有叩荆者。颜熟而不觉。徐诘之。乃原州李汝范也。苍颜相对。叙旧游如昨日事。仍询兄事。汝范言其衰相颇多。神用亦减云。听之。不觉喟然而叹也。意谓以兄禀得之厚。涵养之久。何至如此。如我者蒲柳先枯。无足道也。今以来书。圭复参證。非但教以所业不如前。辞旨间。多有廓落不偶之意。无少及此边一事。无乃深造自得之蕴。不足为愚弟发耶。夫子吾不复梦见周公注。兄可记得。行道存道。实有所不同。此正吾辈今日所可勉处。兄以为如何。弟丧病馀生。外烁内消。苟保性命。然平生畏谨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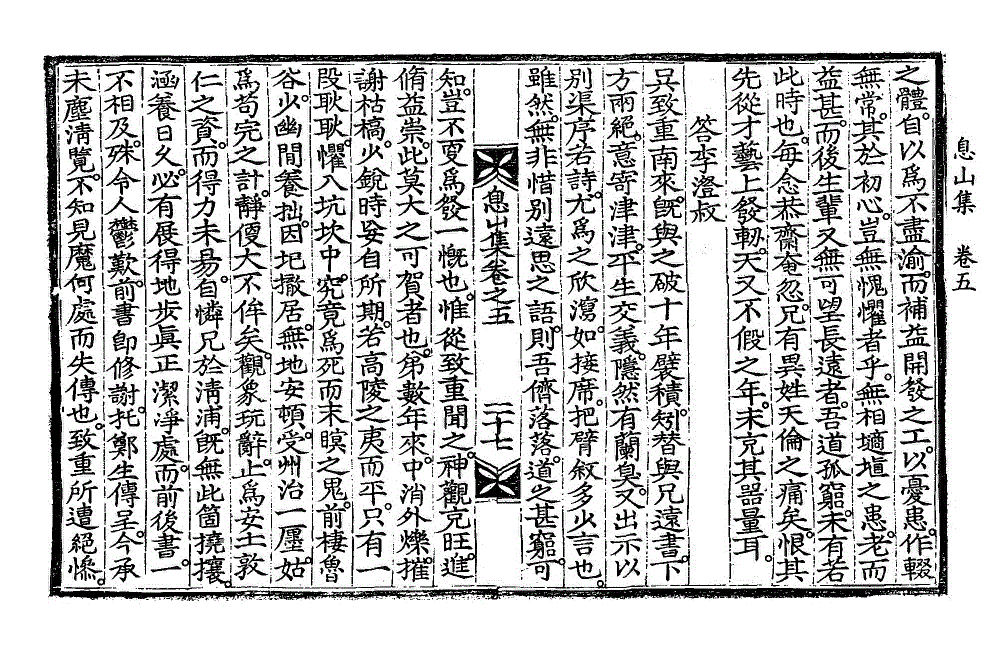 之体。自以为不尽渝。而补益开发之工。以忧患。作辍无常。其于初心。岂无愧惧者乎。无相擿埴之患。老而益甚。而后生辈又无可望长远者。吾道孤穷。未有若此时也。每念恭斋奄忽。兄有异姓天伦之痛矣。恨其先从才艺上发轫。天又不假之年。未充其器量耳。
之体。自以为不尽渝。而补益开发之工。以忧患。作辍无常。其于初心。岂无愧惧者乎。无相擿埴之患。老而益甚。而后生辈又无可望长远者。吾道孤穷。未有若此时也。每念恭斋奄忽。兄有异姓天伦之痛矣。恨其先从才艺上发轫。天又不假之年。未充其器量耳。答李澄叔
吴致重南来。既与之破十年襞积。矧替与兄远书。下方两绝。意寄津津。平生交义。隐然有兰臭。又出示以别渠序若诗。尤为之欣泻。如接席。把臂叙多少言也。虽然。无非惜别远思之语。则吾侪落落。道之甚穷。可知。岂不更为发一慨也。惟从致重闻之。神观充旺。进脩益崇。此莫大之可贺者也。弟数年来。中消外烁。摧谢枯槁。少锐时妄自所期。若高陵之夷而平。只有一段耿耿。惧入坑坎中。究竟为死而未瞑之鬼。前栖鲁谷。少幽閒养拙。因圮撤居。无地安顿。受州治一廛。姑为苟完之计。静便大不侔矣。观象玩辞。止为安土敦仁之资。而得力未易。自怜兄于清浦。既无此个挠攘。涵养日久。必有展得地步真正洁净处。而前后书。一不相及。殊令人郁叹。前书即修谢。托郑生传呈。今承未尘清览。不知见魔何处而失传也。致重所遭绝惨。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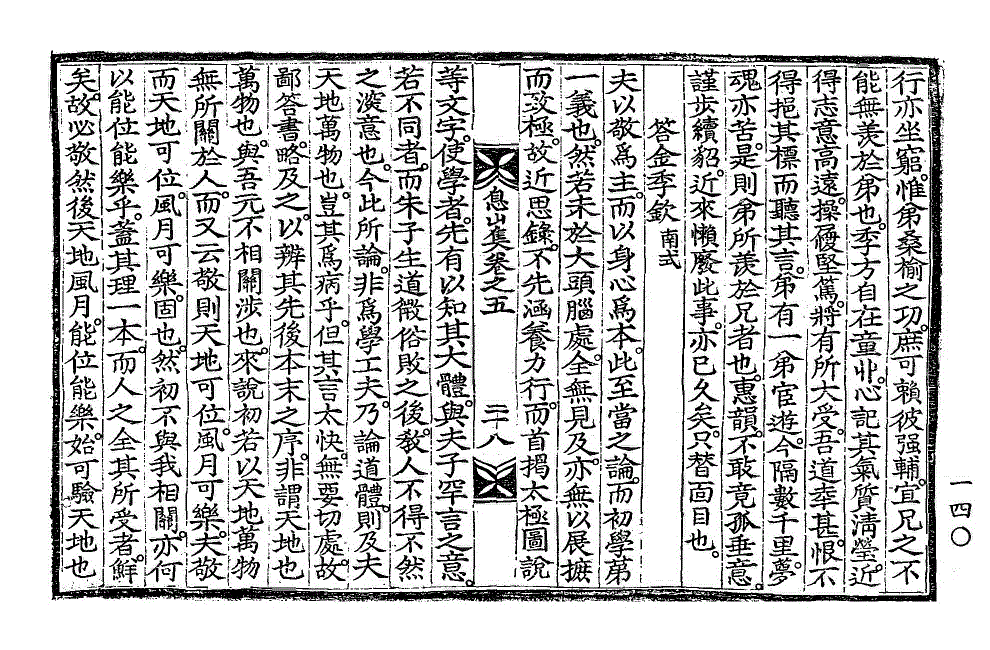 行亦坐穷。惟弟桑榆之功。庶可赖彼强辅。宜兄之不能无羡于弟也。季方自在童丱。心记其气质清莹。近得志意高远。操履坚笃。将有所大受。吾道幸甚。恨不得挹其标而听其言。弟有一弟宦游。今隔数千里。梦魂亦苦。是则弟所羡于兄者也。惠韵。不敢竟孤垂意。谨步续貂。近来懒废此事。亦已久矣。只替面目也。
行亦坐穷。惟弟桑榆之功。庶可赖彼强辅。宜兄之不能无羡于弟也。季方自在童丱。心记其气质清莹。近得志意高远。操履坚笃。将有所大受。吾道幸甚。恨不得挹其标而听其言。弟有一弟宦游。今隔数千里。梦魂亦苦。是则弟所羡于兄者也。惠韵。不敢竟孤垂意。谨步续貂。近来懒废此事。亦已久矣。只替面目也。答金季钦(南式)
夫以敬为主。而以身心为本。此至当之论。而初学第一义也。然若未于大头脑处。全无见及。亦无以展摭而致极。故近思录。不先涵养力行。而首揭太极图说等文字。使学者。先有以知其大体。与夫子罕言之意。若不同者。而朱子生道微俗败之后。教人不得不然之深意也。今此所论。非为学工夫。乃论道体。则及夫天地万物也。岂其为病乎。但其言太快。无要切处。故鄙答书。略及之。以辨其先后本末之序。非谓天地也万物也。与吾元不相关涉也。来说初若以天地万物无所关于人。而又云敬则天地可位。风月可乐。夫敬而天地可位。风月可乐。固也。然初不与我相关。亦何以能位能乐乎。盖其理一本。而人之全其所受者。鲜矣。故必敬然后天地风月。能位能乐。始可验天地也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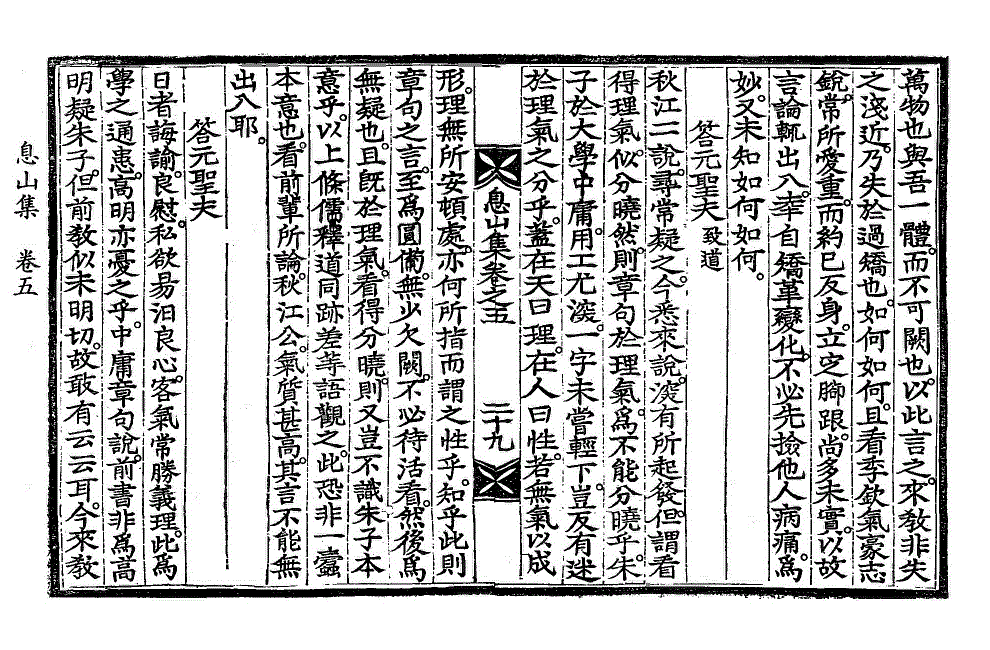 万物也与吾一体。而不可阙也。以此言之。来教非失之浅近。乃失于过矫也。如何如何。且看季钦气豪志锐。常所爱重。而约己反身。立定脚跟。尚多未实。以故言论辄出入。幸自矫革变化。不必先检他人病痛。为妙。又未知如何如何。
万物也与吾一体。而不可阙也。以此言之。来教非失之浅近。乃失于过矫也。如何如何。且看季钦气豪志锐。常所爱重。而约己反身。立定脚跟。尚多未实。以故言论辄出入。幸自矫革变化。不必先检他人病痛。为妙。又未知如何如何。答元圣夫(致道)
秋江二说。寻常疑之。今悉来说。深有所起发。但谓看得理气。似分晓然。则章句于理气。为不能分晓乎。朱子于大学,中庸。用工尤深。一字未尝轻下。岂反有迷于理气之分乎。盖在天曰理。在人曰性。若无气以成形。理无所安顿处。亦何所指而谓之性乎。知乎此则章句之言。至为圆备。无少欠阙。不必待活看。然后为无疑也。且既于理气。看得分晓。则又岂不识朱子本意乎。以上条儒,释道同迹差等语观之。此恐非一蠹本意也。看前辈所论。秋江公。气质甚高。其言不能无出入耶。
答元圣夫
日者诲谕。良慰。私欲易汩良心。客气常胜义理。此为学之通患。高明亦忧之乎。中庸章句说。前书非为高明疑朱子。但前教似未明切。故敢有云云耳。今来教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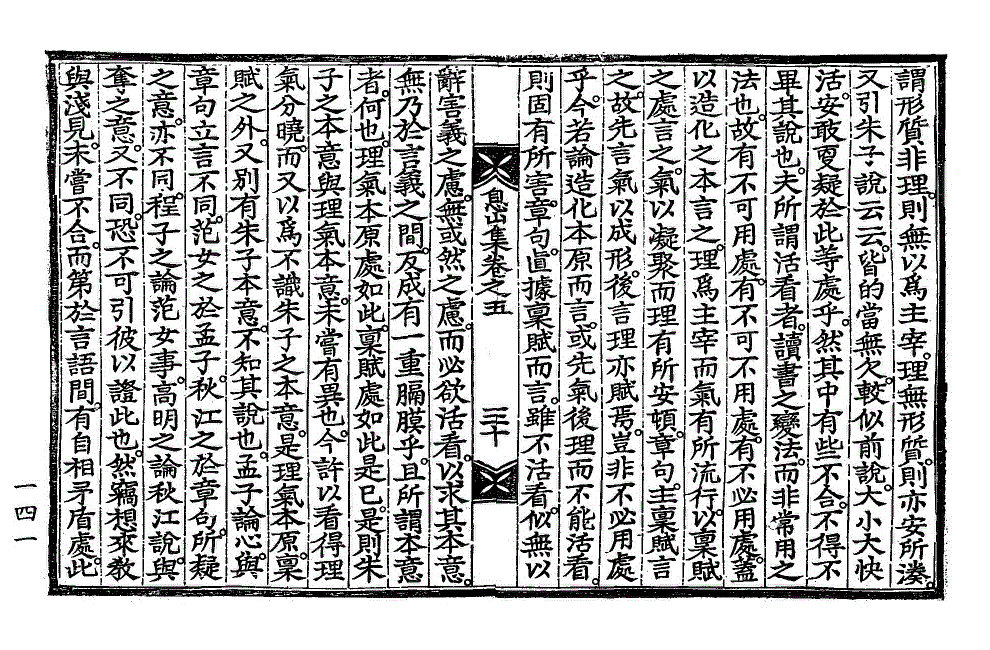 谓形质非理。则无以为主宰。理无形质。则亦安所凑。又引朱子说云云。皆的当无欠。较似前说。大小大快活。安敢更疑于此等处乎。然其中有些不合。不得不毕其说也。夫所谓活看者。读书之变法。而非常用之法也。故有不可用处。有不可不用处。有不必用处。盖以造化之本言之。理为主宰而气有所流行。以禀赋之处言之。气以凝聚而理有所安顿。章句。主禀赋言之。故先言气以成形。后言理亦赋焉。岂非不必用处乎。今若论造化本原而言。或先气后理而不能活看。则固有所害。章句。直据禀赋而言。虽不活看。似无以辞害义之虑。无或然之虑。而必欲活看。以求其本意。无乃于言义之间。反成有一重膈膜乎。且所谓本意者。何也。理气本原处如此。禀赋处如此是已。是则朱子之本意与理气本意。未尝有异也。今许以看得理气分晓。而又以为不识朱子之本意。是理气本原。禀赋之外。又别有朱子本意。不知其说也。孟子论心。与章句立言不同。范女之于孟子。秋江之于章句。所疑之意。亦不同。程子之论范女事。高明之论秋江说。与夺之意。又不同。恐不可引彼以證此也。然窃想来教与浅见。未尝不合。而第于言语间。有自相矛盾处。此
谓形质非理。则无以为主宰。理无形质。则亦安所凑。又引朱子说云云。皆的当无欠。较似前说。大小大快活。安敢更疑于此等处乎。然其中有些不合。不得不毕其说也。夫所谓活看者。读书之变法。而非常用之法也。故有不可用处。有不可不用处。有不必用处。盖以造化之本言之。理为主宰而气有所流行。以禀赋之处言之。气以凝聚而理有所安顿。章句。主禀赋言之。故先言气以成形。后言理亦赋焉。岂非不必用处乎。今若论造化本原而言。或先气后理而不能活看。则固有所害。章句。直据禀赋而言。虽不活看。似无以辞害义之虑。无或然之虑。而必欲活看。以求其本意。无乃于言义之间。反成有一重膈膜乎。且所谓本意者。何也。理气本原处如此。禀赋处如此是已。是则朱子之本意与理气本意。未尝有异也。今许以看得理气分晓。而又以为不识朱子之本意。是理气本原。禀赋之外。又别有朱子本意。不知其说也。孟子论心。与章句立言不同。范女之于孟子。秋江之于章句。所疑之意。亦不同。程子之论范女事。高明之论秋江说。与夺之意。又不同。恐不可引彼以證此也。然窃想来教与浅见。未尝不合。而第于言语间。有自相矛盾处。此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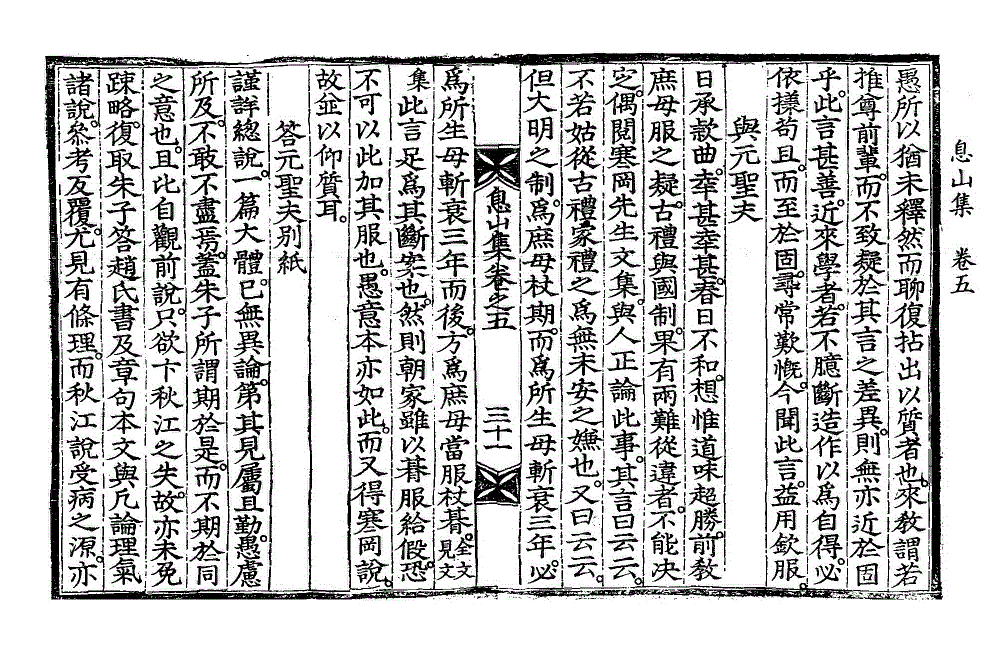 愚所以犹未释然而聊复拈出以质者也。来教谓若推尊前辈。而不致疑于其言之差异。则无亦近于固乎。此言甚善。近来学者。若不臆断造作以为自得。必依㨾苟且。而至于固。寻常叹慨。今闻此言。益用钦服。
愚所以犹未释然而聊复拈出以质者也。来教谓若推尊前辈。而不致疑于其言之差异。则无亦近于固乎。此言甚善。近来学者。若不臆断造作以为自得。必依㨾苟且。而至于固。寻常叹慨。今闻此言。益用钦服。与元圣夫
日承款曲。幸甚幸甚。春日不和。想惟道味超胜。前教庶母服之疑。古礼与国制。果有两难从违者。不能决定。偶阅寒冈先生文集。与人正论此事。其言曰云云。不若姑从古礼,家礼之为无未安之嫌也。又曰云云。但大明之制。为庶母杖期。而为所生母斩衰三年。必为所生母斩衰三年而后。方为庶母当服杖期。(全文见文集)此言足为其断案也。然则朝家虽以期服给假。恐不可以此加其服也。愚意本亦如此。而又得寒冈说。故并以仰质耳。
答元圣夫别纸
谨详总说。一篇大体。已无异论。第其见属且勤。愚虑所及。不敢不尽焉。盖朱子所谓期于是。而不期于同之意也。且比自观前说。只欲卞秋江之失。故亦未免疏略。复取朱子答赵氏书及章句本文与凡论理气诸说。参考反覆。尤见有条理。而秋江说受病之源。亦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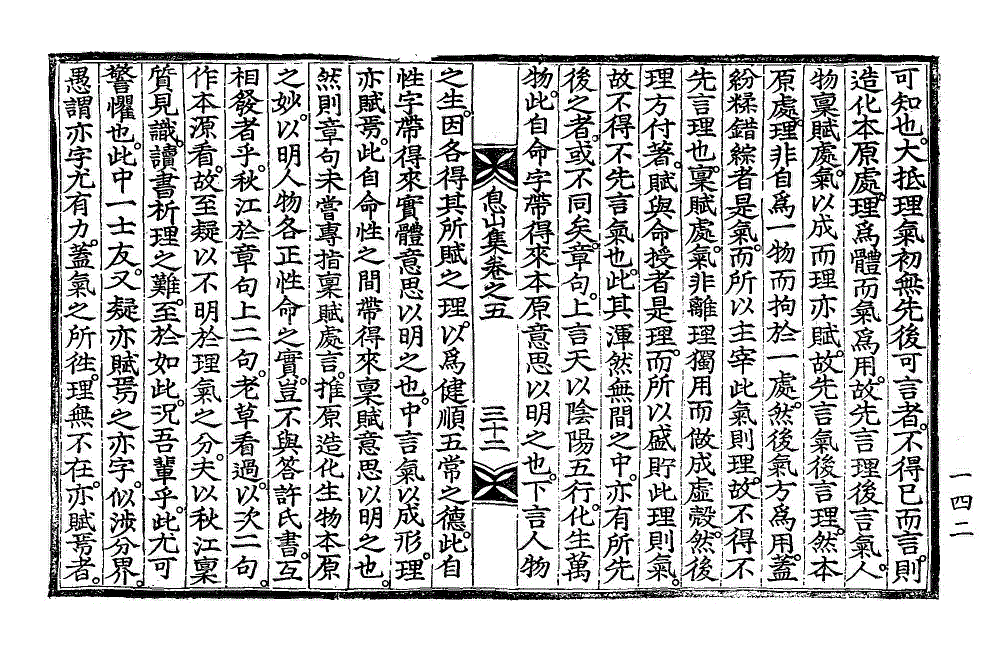 可知也。大抵理气初无先后可言者。不得已而言。则造化本原处。理为体而气为用。故先言理后言气。人物禀赋处。气以成而理亦赋。故先言气后言理。然本原处。理非自为一物而拘于一处。然后气方为用。盖纷糅错综者是气。而所以主宰此气则理。故不得不先言理也。禀赋处。气非离理独用而做成虚壳。然后理方付著。赋与命授者是理。而所以盛贮此理则气。故不得不先言气也。此其浑然无间之中。亦有所先后之者。或不同矣。章句。上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此自命字带得来本原意思以明之也。下言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此自性字带得来实体意思以明之也。中言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此自命性之间带得来禀赋意思以明之也。然则章句未尝专指禀赋处言。推原造化生物本原之妙。以明人物各正性命之实。岂不与答许氏书。互相发者乎。秋江于章句上二句。老草看过。以次二句。作本源看。故至疑以不明于理气之分。夫以秋江禀质见识。读书析理之难。至于如此。况吾辈乎。此尤可警惧也。此中一士友。又疑亦赋焉之亦字。似涉分界。愚谓亦字尤有力。盖气之所往。理无不在。亦赋焉者。
可知也。大抵理气初无先后可言者。不得已而言。则造化本原处。理为体而气为用。故先言理后言气。人物禀赋处。气以成而理亦赋。故先言气后言理。然本原处。理非自为一物而拘于一处。然后气方为用。盖纷糅错综者是气。而所以主宰此气则理。故不得不先言理也。禀赋处。气非离理独用而做成虚壳。然后理方付著。赋与命授者是理。而所以盛贮此理则气。故不得不先言气也。此其浑然无间之中。亦有所先后之者。或不同矣。章句。上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此自命字带得来本原意思以明之也。下言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此自性字带得来实体意思以明之也。中言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此自命性之间带得来禀赋意思以明之也。然则章句未尝专指禀赋处言。推原造化生物本原之妙。以明人物各正性命之实。岂不与答许氏书。互相发者乎。秋江于章句上二句。老草看过。以次二句。作本源看。故至疑以不明于理气之分。夫以秋江禀质见识。读书析理之难。至于如此。况吾辈乎。此尤可警惧也。此中一士友。又疑亦赋焉之亦字。似涉分界。愚谓亦字尤有力。盖气之所往。理无不在。亦赋焉者。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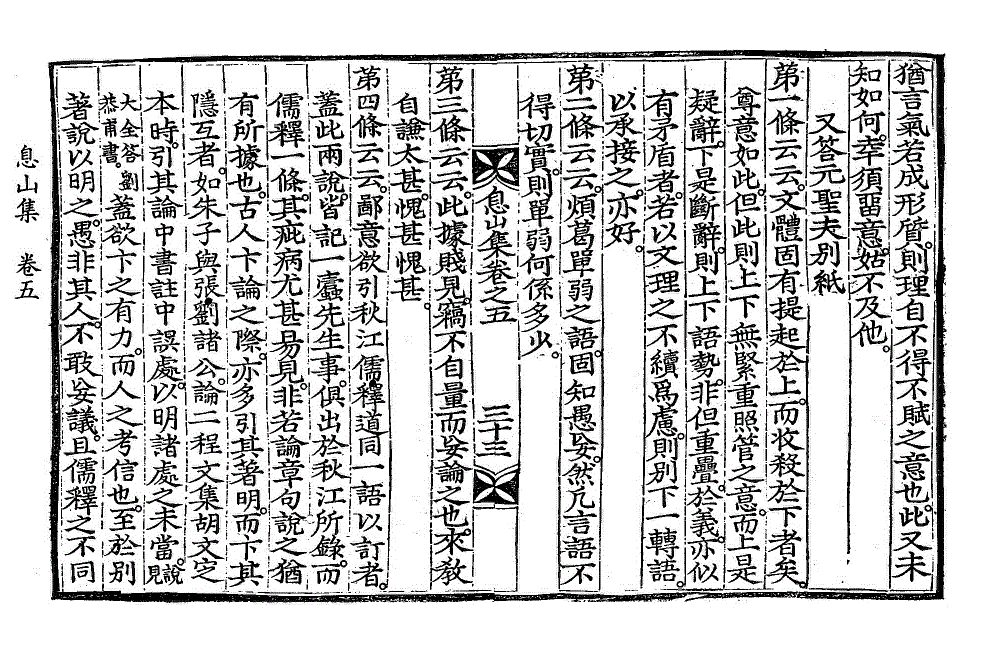 犹言气若成形质。则理自不得不赋之意也。此又未知如何。幸须留意。姑不及他。
犹言气若成形质。则理自不得不赋之意也。此又未知如何。幸须留意。姑不及他。又答元圣夫别纸
第一条云云。文体固有提起于上。而收杀于下者矣。尊意如此。但此则上下无紧重照管之意。而上是疑辞。下是断辞。则上下语势。非但重叠。于义。亦似有矛盾者。若以文理之不续为虑。则别下一转语。以承接之。亦好。
第二条云云。烦葛单弱之语。固知愚妄。然凡言语不得切实。则单弱何系多少。
第三条云云。此据贱见。窃不自量而妄论之也。来教自谦太甚。愧甚愧甚。
第四条云云。鄙意欲引秋江儒,释道同一语以订者。盖此两说。皆记一蠹先生事。俱出于秋江所录。而儒释一条。其疵病尤甚易见。非若论章句说之犹有所据也。古人卞论之际。亦多引其著明。而卞其隐互者。如朱子与张,刘诸公。论二程文集胡文定本时。引其论中书注中误处。以明诸处之未当。(说见大全答刘恭甫书。)盖欲卞之有力。而人之考信也。至于别著说以明之。愚非其人。不敢妄议。且儒释之不同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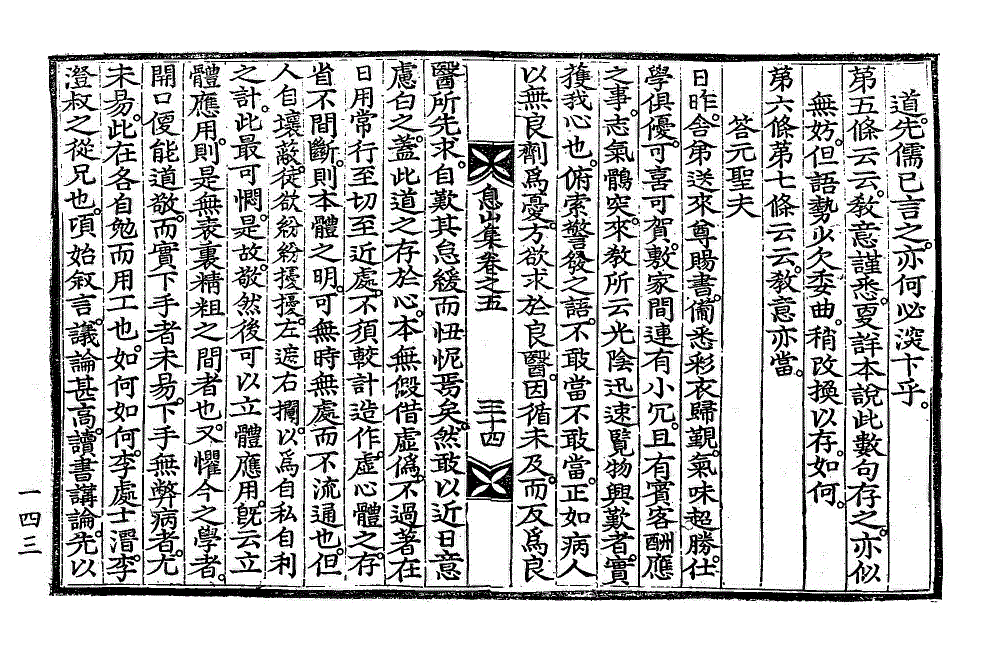 道。先儒已言之。亦何必深卞乎。
道。先儒已言之。亦何必深卞乎。第五条云云。教意谨悉。更详本说此数句存之。亦似无妨。但语势少欠委曲。稍改换以存。如何。
第六条第七条云云。教意亦当。
答元圣夫
日昨。舍弟送来尊赐书。备悉彩衣归觐。气味超胜。仕学俱优。可喜可贺。敷家间连有小冗。且有宾客酬应之事。志气鹘突。来教所云光阴迅速览物兴叹者。实获我心也。俯索警发之语。不敢当不敢当。正如病人以无良剂为忧。方欲求于良医。因循未及。而反为良医所先求。自叹其怠缓而忸怩焉矣。然敢以近日意虑白之。盖此道之存于心。本无假借虚伪。不过著在日用常行至切至近处。不须较计造作。虚心体之。存省不间断。则本体之明。可无时无处而不流通也。但人自坏蔽。徒欲纷纷扰扰。左遮右拦。以为自私自利之计。此最可悯。是故。敬然后可以立体应用。既云立体应用。则是无表里精粗之间者也。又惧今之学者。开口便能道敬。而实下手者未易。下手无弊病者。尤未易。此在各自勉而用工也。如何如何。李处士溍。李澄叔之从兄也。顷始叙言。议论甚高。读书讲论。先以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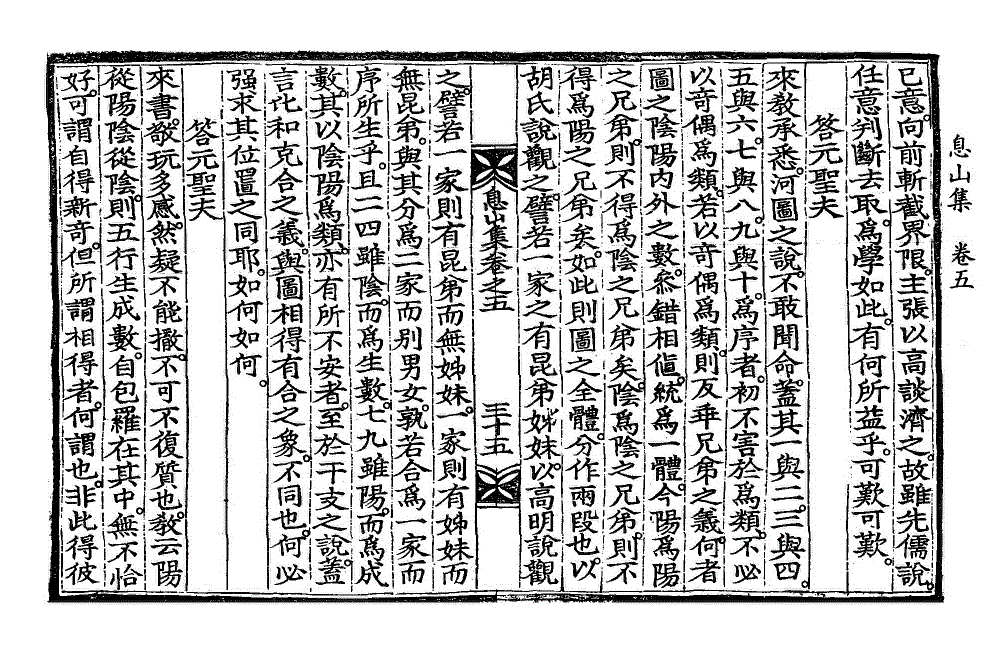 己意。向前斩截界限。主张以高谈济之。故虽先儒说。任意判断去取。为学如此。有何所益乎。可叹可叹。
己意。向前斩截界限。主张以高谈济之。故虽先儒说。任意判断去取。为学如此。有何所益乎。可叹可叹。答元圣夫
来教承悉。河图之说。不敢闻命。盖其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为序者。初不害于为类。不必以奇偶为类。若以奇偶为类。则反乖兄弟之义。何者图之阴阳内外之数。参错相值。统为一体。今阳为阳之兄弟。则不得为阴之兄弟矣。阴为阴之兄弟。则不得为阳之兄弟矣。如此则图之全体。分作两段也。以胡氏说观之。譬若一家之有昆弟姊妹。以高明说观之。譬若一家则有昆弟而无姊妹。一家则有姊妹而无昆弟。与其分为二家而别男女。孰若合为一家而序所生乎。且二四虽阴。而为生数。七九虽阳。而为成数。其以阴阳为类。亦有所不安者。至于干支之说。盖言比和克合之义。与图相得有合之象。不同也。何必强求其位置之同耶。如何如何。
答元圣夫
来书。敬玩多感。然疑不能撤。不可不复质也。教云阳从阳阴从阴。则五行生成数。自包罗在其中。无不恰好。可谓自得新奇。但所谓相得者。何谓也。非此得彼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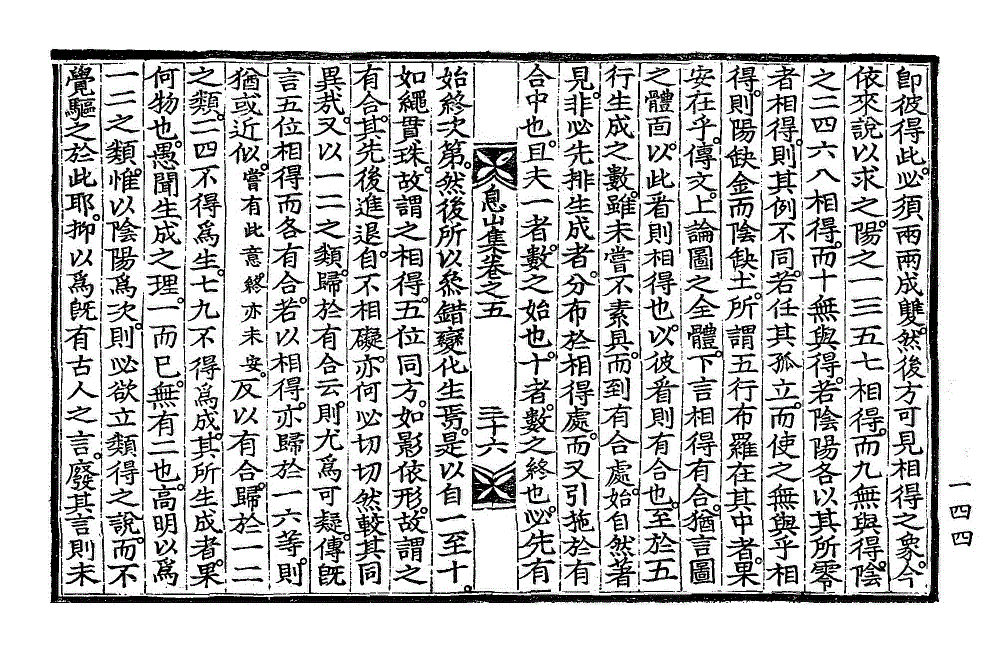 即彼得此。必须两两成双。然后方可见相得之象。今依来说以求之。阳之一三五七相得。而九无与得。阴之二四六八相得。而十无与得。若阴阳各以其所零者相得。则其例不同。若任其孤立。而使之无与乎相得。则阳缺金而阴缺土。所谓五行布罗在其中者。果安在乎。传文。上论图之全体。下言相得有合。犹言图之体面。以此看则相得也。以彼看则有合也。至于五行生成之数。虽未尝不素具。而到有合处。始自然著见。非必先排生成者。分布于相得处。而又引拖于有合中也。且夫一者。数之始也。十者。数之终也。必先有始终次第。然后所以参错变化生焉。是以自一至十。如绳贯珠。故谓之相得。五位同方。如影依形。故谓之有合。其先后进退。自不相碍。亦何必切切然较其同异哉。又以一二之类。归于有合云。则尤为可疑。传既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若以相得。亦归于一六等。则犹或近似。(尝有此意。终亦未安。)反以有合。归于一二之类。二四不得为生。七九不得为成。其所生成者。果何物也。愚闻生成之理。一而已。无有二也。高明以为一二之类。惟以阴阳为次。则必欲立类得之说。而不觉驱之于此耶。抑以为既有古人之言。废其言则未
即彼得此。必须两两成双。然后方可见相得之象。今依来说以求之。阳之一三五七相得。而九无与得。阴之二四六八相得。而十无与得。若阴阳各以其所零者相得。则其例不同。若任其孤立。而使之无与乎相得。则阳缺金而阴缺土。所谓五行布罗在其中者。果安在乎。传文。上论图之全体。下言相得有合。犹言图之体面。以此看则相得也。以彼看则有合也。至于五行生成之数。虽未尝不素具。而到有合处。始自然著见。非必先排生成者。分布于相得处。而又引拖于有合中也。且夫一者。数之始也。十者。数之终也。必先有始终次第。然后所以参错变化生焉。是以自一至十。如绳贯珠。故谓之相得。五位同方。如影依形。故谓之有合。其先后进退。自不相碍。亦何必切切然较其同异哉。又以一二之类。归于有合云。则尤为可疑。传既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若以相得。亦归于一六等。则犹或近似。(尝有此意。终亦未安。)反以有合。归于一二之类。二四不得为生。七九不得为成。其所生成者。果何物也。愚闻生成之理。一而已。无有二也。高明以为一二之类。惟以阴阳为次。则必欲立类得之说。而不觉驱之于此耶。抑以为既有古人之言。废其言则未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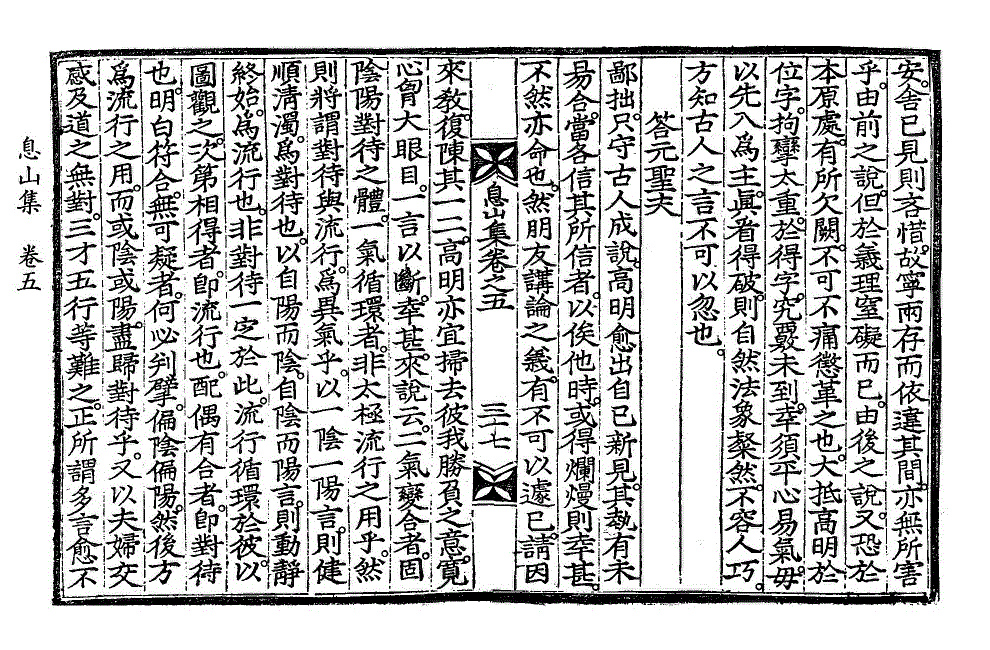 安。舍己见则吝惜。故宁两存而依违其间。亦无所害乎。由前之说。但于义理窒碍而已。由后之说。又恐于本原处。有所欠阙。不可不痛惩革之也。大抵高明于位字。拘挛太重。于得字。究覈未到。幸须平心易气。毋以先入为主。真看得破。则自然法象粲然。不容人巧。方知古人之言不可以忽也。
安。舍己见则吝惜。故宁两存而依违其间。亦无所害乎。由前之说。但于义理窒碍而已。由后之说。又恐于本原处。有所欠阙。不可不痛惩革之也。大抵高明于位字。拘挛太重。于得字。究覈未到。幸须平心易气。毋以先入为主。真看得破。则自然法象粲然。不容人巧。方知古人之言不可以忽也。答元圣夫
鄙拙。只守古人成说。高明愈出自己新见。其势有未易合。当各信其所信者。以俟他时。或得烂熳则幸甚。不然亦命也。然朋友讲论之义。有不可以遽已。请因来教。复陈其一二。高明亦宜扫去彼我胜负之意。宽心胸大眼目。一言以断。幸甚。来说云。二气变合者。固阴阳对待之体。一气循环者。非太极流行之用乎。然则将谓对待与流行。为异气乎。以一阴一阳言。则健顺清浊。为对待也。以自阳而阴。自阴而阳言。则动静终始。为流行也。非对待一定于此。流行循环于彼。以图观之。次第相得者。即流行也。配偶有合者。即对待也。明白符合。无可疑者。何必判擘。偏阴偏阳。然后方为流行之用。而或阴或阳。尽归对待乎。又以夫妇交感及道之无对。三才五行等难之。正所谓多言愈不
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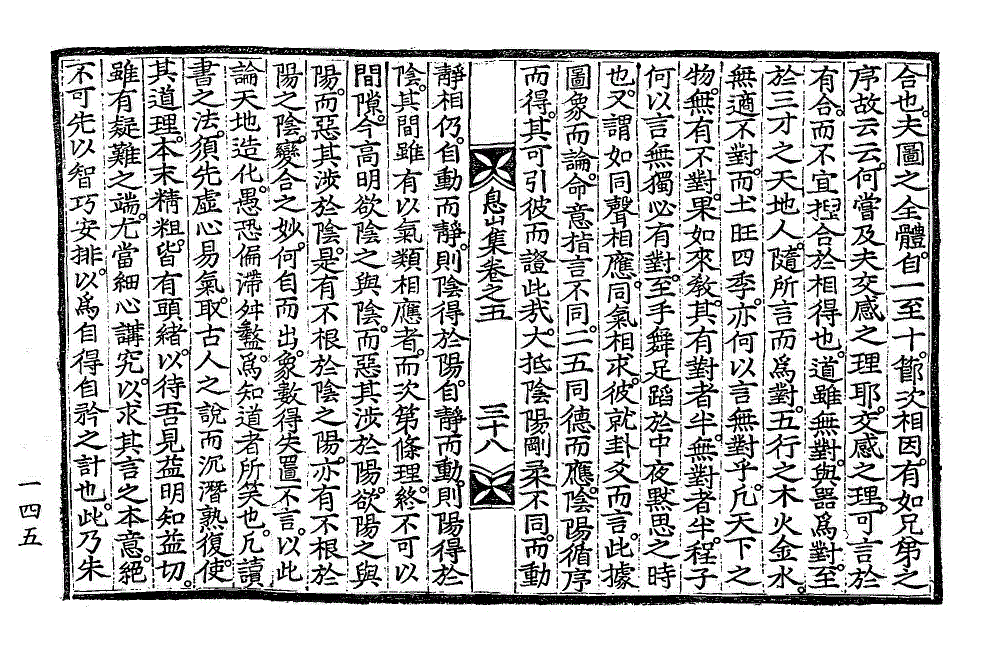 合也。夫图之全体。自一至十。节次相因。有如兄弟之序故云云。何尝及夫交感之理耶。交感之理。可言于有合。而不宜捏合于相得也。道虽无对。与器为对。至于三才之天地人。随所言而为对。五行之木火金水。无适不对。而土旺四季。亦何以言无对乎。凡天下之物。无有不对。果如来教。其有对者半。无对者半。程子何以言无独必有对。至手舞足蹈于中夜默思之时也。又谓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就卦爻而言。此据图象而论。命意指言不同。二五同德而应。阴阳循序而得。其可引彼而證此哉。大抵阴阳刚柔不同。而动静相仍。自动而静。则阴得于阳。自静而动。则阳得于阴。其间虽有以气类相应者。而次第条理。终不可以间隙。今高明欲阴之与阴。而恶其涉于阳。欲阳之与阳。而恶其涉于阴。是有不根于阴之阳。亦有不根于阳之阴。变合之妙。何自而出。象数得失置不言。以此论天地造化。愚恐偏滞舛盭。为知道者所笑也。凡读书之法。须先虚心易气。取古人之说而沉潜熟复。使其道理。本末精粗。皆有头绪。以待吾见益明知益切。虽有疑难之端。尤当细心讲究。以求其言之本意。绝不可先以智巧安排。以为自得自矜之计也。此乃朱
合也。夫图之全体。自一至十。节次相因。有如兄弟之序故云云。何尝及夫交感之理耶。交感之理。可言于有合。而不宜捏合于相得也。道虽无对。与器为对。至于三才之天地人。随所言而为对。五行之木火金水。无适不对。而土旺四季。亦何以言无对乎。凡天下之物。无有不对。果如来教。其有对者半。无对者半。程子何以言无独必有对。至手舞足蹈于中夜默思之时也。又谓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就卦爻而言。此据图象而论。命意指言不同。二五同德而应。阴阳循序而得。其可引彼而證此哉。大抵阴阳刚柔不同。而动静相仍。自动而静。则阴得于阳。自静而动。则阳得于阴。其间虽有以气类相应者。而次第条理。终不可以间隙。今高明欲阴之与阴。而恶其涉于阳。欲阳之与阳。而恶其涉于阴。是有不根于阴之阳。亦有不根于阳之阴。变合之妙。何自而出。象数得失置不言。以此论天地造化。愚恐偏滞舛盭。为知道者所笑也。凡读书之法。须先虚心易气。取古人之说而沉潜熟复。使其道理。本末精粗。皆有头绪。以待吾见益明知益切。虽有疑难之端。尤当细心讲究。以求其言之本意。绝不可先以智巧安排。以为自得自矜之计也。此乃朱息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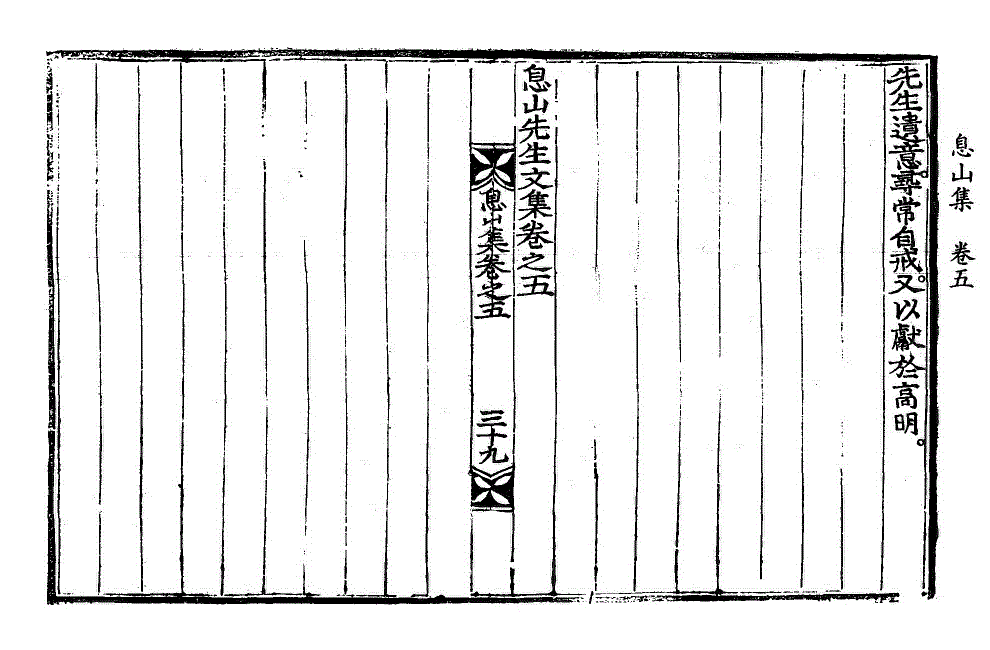 先生遗意。寻常自戒。又以献于高明。
先生遗意。寻常自戒。又以献于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