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圃阴集卷之六 第 x 页
圃阴集卷之六(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序
序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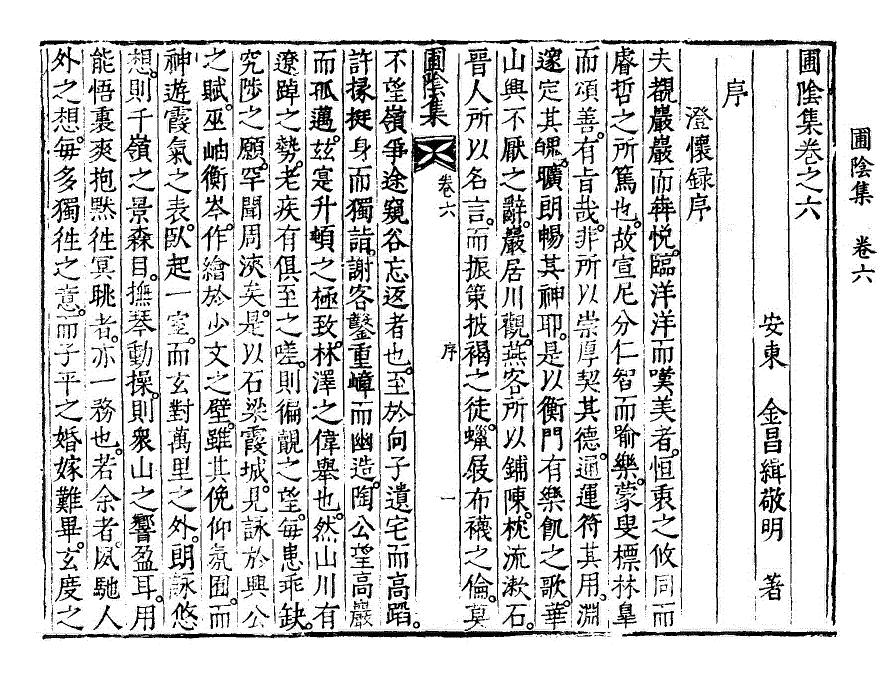 澄怀录序
澄怀录序夫睹岩岩而奔悦。临洋洋而叹美者。恒衷之攸同而睿哲之所笃也。故宣尼分仁智而喻乐。蒙叟标林皋而颂善。有旨哉。非所以崇厚契其德。通运符其用。渊邃定其魄。旷朗畅其神耶。是以衡门有乐饥之歌。华山兴不厌之辞。岩居川观。燕客所以铺陈。枕流漱石。晋人所以名言。而振策披褐之徒。蜡屐布袜之伦。莫不望岭争途窥谷忘返者也。至于向子遗宅而高蹈。许掾挺身而独诣。谢客凿重嶂而幽造。陶公望高岩而孤迈。玆寔升顿之极致。林泽之伟举也。然山川有辽踔之势。老疾有俱至之嗟。则遍觌之望。每患乖缺。究陟之愿。罕闻周浃矣。是以石梁霞城。见咏于兴公之赋。巫岫衡岑。作绘于少文之壁。虽其俛仰氛囿。而神游霞气之表。卧起一室。而玄对万里之外。朗咏悠想。则千岭之景森目。抚琴动操。则众山之响盈耳。用能悟里爽抱默往冥眺者。亦一务也。若余者。夙驰人外之想。每多独往之意。而子平之婚嫁难毕。玄度之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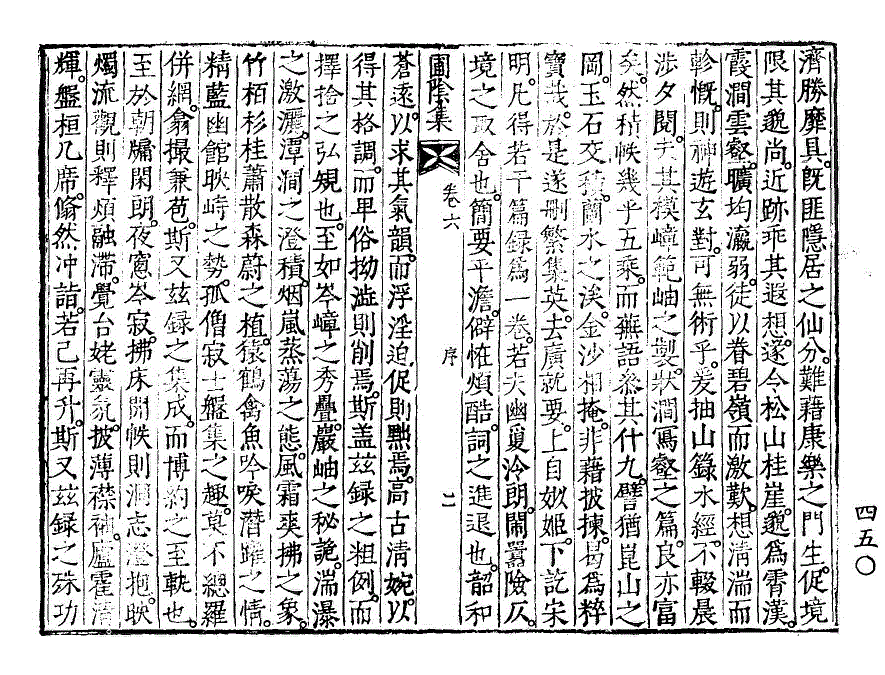 济胜靡具。既匪隐居之仙分。难藉康乐之门生。促境限其邈尚。近迹乖其遐想。遂令松山桂崖。邈为霄汉。霞涧云壑。旷均瀛弱。徒以眷碧岭而激叹。想清湍而轸慨。则神游玄对。可无术乎。爰抽山箓水经。不辍晨涉夕阅。夫其模嶂范岫之制。状涧写壑之篇。良亦富矣。然积帙几乎五乘。而芜语参其什九。譬犹昆山之冈。玉石交积。兰水之涘。金沙相掩。非藉披拣。曷为粹宝哉。于是遂删繁集英。去广就要。上自姒姬。下讫宋明。凡得若干篇录为一卷。若夫幽夐泠朗。闹嚣险仄。境之取舍也。简要平澹。僻怪烦酷。词之进退也。韶和苍远。以求其气韵。而浮淫迫促则黜焉。高古清婉。以得其格调。而卑俗拗涩则削焉。斯盖玆录之粗例。而择舍之弘规也。至如岑嶂之秀叠。岩岫之秘诡。湍瀑之激洒。潭涧之澄积。烟岚蒸荡之态。风霜爽拂之象。竹柏杉桂萧散森蔚之植。猿鹤禽鱼吟唳潜跃之情。精蓝幽馆映峙之势。孤僧寂士盘集之趣。莫不总罗并网。翕撮兼苞。斯又玆录之集成。而博约之至轨也。至于朝牖闲朗。夜窗岑寂。拂床开帙则洞志澄抱。映烛流观则释烦融滞。觉台姥灵氛。披薄襟袖。庐霍清辉。盘桓几席。翛然冲诣。若己再升。斯又玆录之殊功
济胜靡具。既匪隐居之仙分。难藉康乐之门生。促境限其邈尚。近迹乖其遐想。遂令松山桂崖。邈为霄汉。霞涧云壑。旷均瀛弱。徒以眷碧岭而激叹。想清湍而轸慨。则神游玄对。可无术乎。爰抽山箓水经。不辍晨涉夕阅。夫其模嶂范岫之制。状涧写壑之篇。良亦富矣。然积帙几乎五乘。而芜语参其什九。譬犹昆山之冈。玉石交积。兰水之涘。金沙相掩。非藉披拣。曷为粹宝哉。于是遂删繁集英。去广就要。上自姒姬。下讫宋明。凡得若干篇录为一卷。若夫幽夐泠朗。闹嚣险仄。境之取舍也。简要平澹。僻怪烦酷。词之进退也。韶和苍远。以求其气韵。而浮淫迫促则黜焉。高古清婉。以得其格调。而卑俗拗涩则削焉。斯盖玆录之粗例。而择舍之弘规也。至如岑嶂之秀叠。岩岫之秘诡。湍瀑之激洒。潭涧之澄积。烟岚蒸荡之态。风霜爽拂之象。竹柏杉桂萧散森蔚之植。猿鹤禽鱼吟唳潜跃之情。精蓝幽馆映峙之势。孤僧寂士盘集之趣。莫不总罗并网。翕撮兼苞。斯又玆录之集成。而博约之至轨也。至于朝牖闲朗。夜窗岑寂。拂床开帙则洞志澄抱。映烛流观则释烦融滞。觉台姥灵氛。披薄襟袖。庐霍清辉。盘桓几席。翛然冲诣。若己再升。斯又玆录之殊功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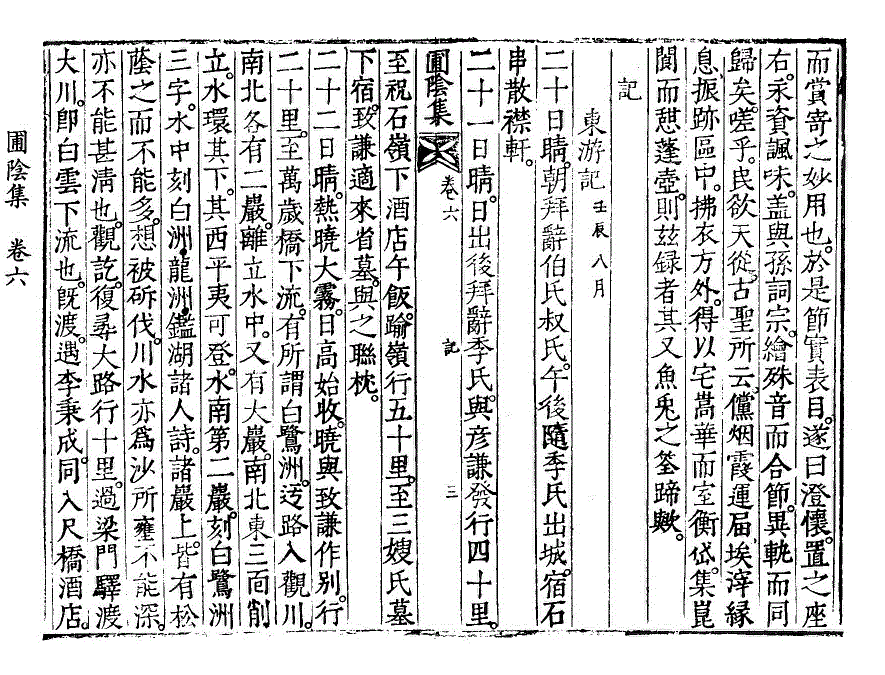 而赏寄之妙用也。于是节实表目。遂曰澄怀。置之座右。永资讽味。盖与孙词宗。绘殊音而合节。异轨而同归矣。嗟乎。民欲天从。古圣所云。傥烟霞运届。埃滓缘息。振迹区中。拂衣方外。得以宅嵩华而室衡岱。集昆阆而憩蓬壶。则玆录者其又鱼兔之筌蹄欤。
而赏寄之妙用也。于是节实表目。遂曰澄怀。置之座右。永资讽味。盖与孙词宗。绘殊音而合节。异轨而同归矣。嗟乎。民欲天从。古圣所云。傥烟霞运届。埃滓缘息。振迹区中。拂衣方外。得以宅嵩华而室衡岱。集昆阆而憩蓬壶。则玆录者其又鱼兔之筌蹄欤。圃阴集卷之六(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记
东游记
壬辰八月
二十日睛(一作晴)。朝拜辞伯氏叔氏。午后随季氏出城。宿石串散襟轩。
二十一日晴。日出后拜辞季氏。与彦谦发行四十里。至祝石岭下酒店午饭。踰岭行五十里。至三嫂氏墓下宿。致谦适来省墓。与之联枕。
二十二日晴。热晓大雾。日高始收。晓与致谦作别。行二十里。至万岁桥下流。有所谓白鹭洲。迂路入观川。南北各有二岩。离立水中。又有大岩。南北东三面削立。水环其下。其西平夷可登。水南第二岩。刻白鹭洲三字。水中刻白洲,龙洲,鉴湖诸人诗。诸岩上。皆有松荫之而不能多。想被䂨伐。川水亦为沙所壅不能深。亦不能甚清也。观讫。复寻大路行十里。过梁门驿渡大川。即白云下流也。既渡。遇李秉成。同入尺桥酒店。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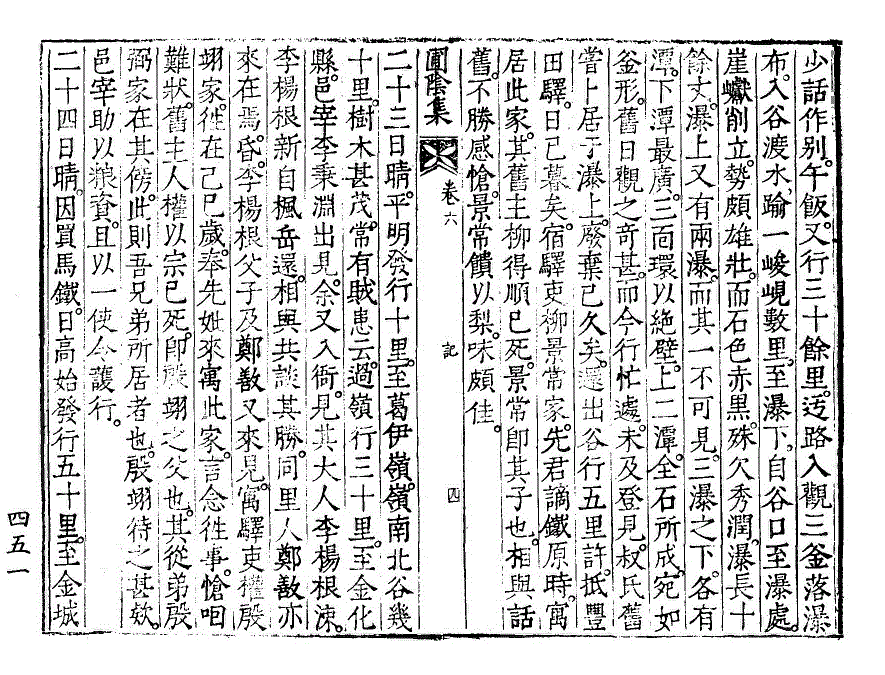 少话作别。午饭。又行三十馀里。迂路入观三釜落瀑布。入谷渡水。踰一峻岘数里。至瀑下。自谷口至瀑处。崖巘削立。势颇雄壮。而石色赤黑。殊欠秀润。瀑长十馀丈。瀑上又有两瀑。而其一不可见。三瀑之下。各有潭。下潭最广。三面环以绝壁。上二潭。全石所成。宛如釜形。旧日观之奇甚。而今行忙遽。未及登见。叔氏旧尝卜居于瀑上。废弃已久矣。还出谷行五里许。抵丰田驿。日已暮矣。宿驿吏柳景常家。先君谪铁原时。寓居此家。其旧主柳得顺已死。景常即其子也。相与话旧。不胜感怆。景常馈以梨。味颇佳。
少话作别。午饭。又行三十馀里。迂路入观三釜落瀑布。入谷渡水。踰一峻岘数里。至瀑下。自谷口至瀑处。崖巘削立。势颇雄壮。而石色赤黑。殊欠秀润。瀑长十馀丈。瀑上又有两瀑。而其一不可见。三瀑之下。各有潭。下潭最广。三面环以绝壁。上二潭。全石所成。宛如釜形。旧日观之奇甚。而今行忙遽。未及登见。叔氏旧尝卜居于瀑上。废弃已久矣。还出谷行五里许。抵丰田驿。日已暮矣。宿驿吏柳景常家。先君谪铁原时。寓居此家。其旧主柳得顺已死。景常即其子也。相与话旧。不胜感怆。景常馈以梨。味颇佳。二十三日晴。平明发行十里。至葛伊岭。岭南北谷几十里。树木甚茂。常有贼患云。过岭行三十里。至金化县。邑宰李秉渊出见。余又入衙。见其大人李杨根涑。李杨根新自枫岳还。相与共谈其胜。同里人郑㪨亦来在焉。昏。李杨根父子及郑㪨又来见。寓驿吏权殷翊家。往在己巳岁。奉先妣来寓此家。言念往事。怆咽难状。旧主人权以宗已死。即殷翊之父也。其从弟殷弼家在其傍。此则吾兄弟所居者也。殷翊待之甚款。邑宰助以粮资。且以一使令护行。
二十四日晴。因买马铁。日高始发行五十里。至金城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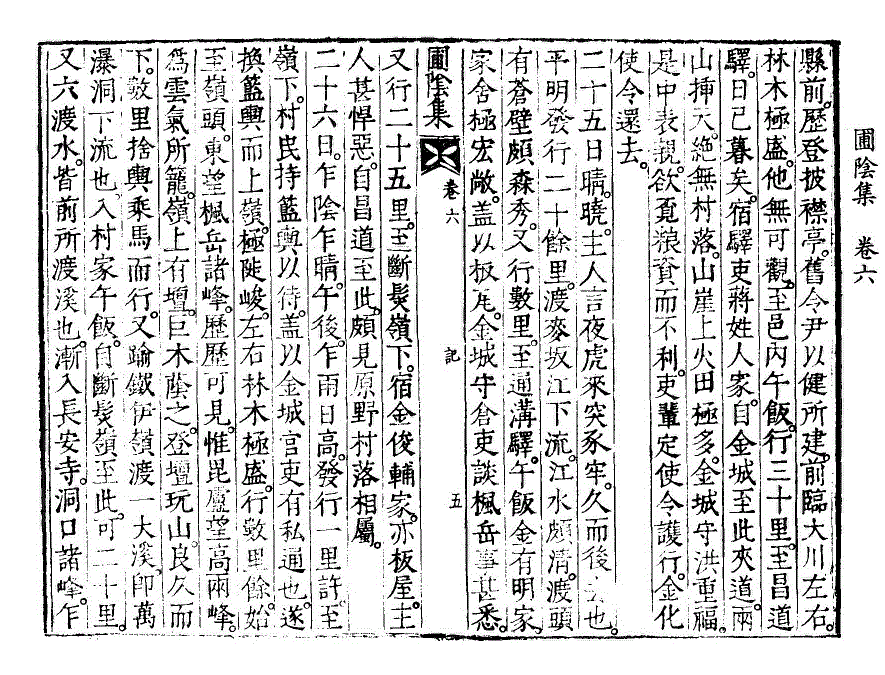 县前。历登披襟亭。旧令尹以健所建。前临大川左右。林木极盛。他无可观。至邑内午饭。行三十里。至昌道驿。日已暮矣。宿驿吏蒋姓人家。自金城至此夹道。两山插天。绝无村落。山崖上火田极多。金城守洪重福。是中表亲。欲觅粮资而不利。吏辈定使令护行。金化使令还去。
县前。历登披襟亭。旧令尹以健所建。前临大川左右。林木极盛。他无可观。至邑内午饭。行三十里。至昌道驿。日已暮矣。宿驿吏蒋姓人家。自金城至此夹道。两山插天。绝无村落。山崖上火田极多。金城守洪重福。是中表亲。欲觅粮资而不利。吏辈定使令护行。金化使令还去。二十五日晴。晓。主人言夜虎来突豕牢。久而后去也。平明发行二十馀里。渡麦坂江下流。江水颇清。渡头有苍壁颇森秀。又行数里。至通沟驿。午饭金有明家。家舍极宏敞。盖以板瓦。金城守仓吏谈枫岳事甚悉。又行二十五里。至断发岭下。宿金俊辅家。亦板屋。主人甚悍恶。自昌道至此。颇见原野村落相属。
二十六日。乍阴乍晴。午后。乍雨日高。发行一里许。至岭下。村民持篮舆以待。盖以金城官吏有私通也。遂换篮舆而上岭。极陡峻。左右林木极盛。行数里馀。始至岭头。东望枫岳诸峰。历历可见。惟毗卢望高两峰。为云气所笼。岭上有坛。巨木荫之。登坛玩山。良久而下。数里舍舆乘马而行。又踰铁伊岭渡一大溪。即万瀑洞下流也。入村家午饭。自断发岭至此。可二十里。又六渡水。皆前所渡溪也。渐入长安寺。洞口诸峰。乍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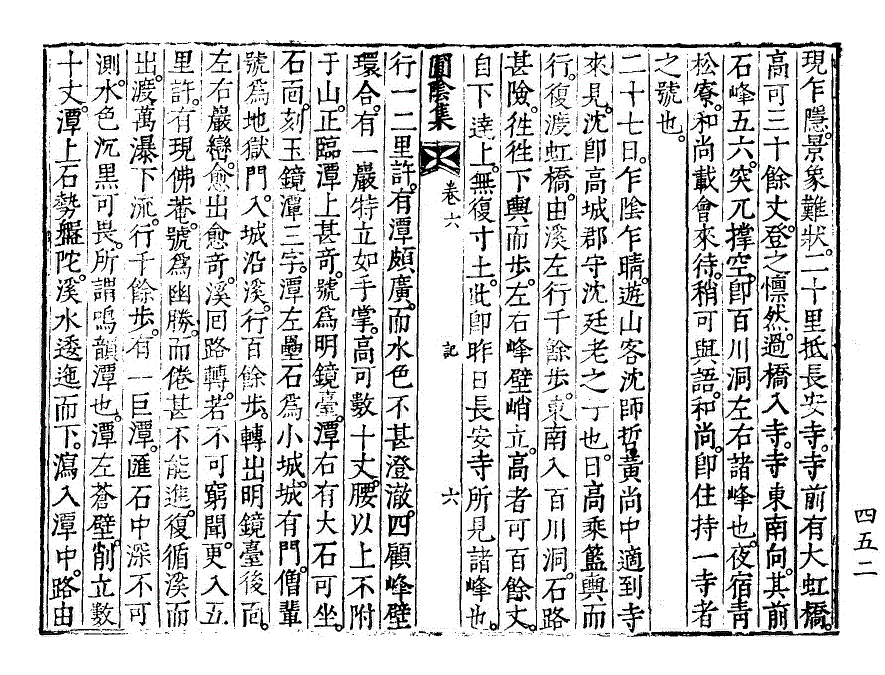 现乍隐。景象难状。二十里抵长安寺。寺前有大虹桥。高可三十馀丈。登之懔然。过桥入寺。寺东南向。其前石峰五六。突兀撑空。即百川洞左右诸峰也。夜宿青松寮。和尚载会来待。稍可与语。和尚。即住持一寺者之号也。
现乍隐。景象难状。二十里抵长安寺。寺前有大虹桥。高可三十馀丈。登之懔然。过桥入寺。寺东南向。其前石峰五六。突兀撑空。即百川洞左右诸峰也。夜宿青松寮。和尚载会来待。稍可与语。和尚。即住持一寺者之号也。二十七日。乍阴乍晴。游山客沈师哲,黄尚中适到寺来见。沈即高城郡守沈廷老之子也。日高乘篮舆而行。复渡虹桥。由溪左行千馀步。东南入百川洞。石路甚险。往往下舆而步。左右峰壁峭立。高者可百馀丈。自下达上。无复寸土。此即昨日长安寺所见诸峰也。行一二里许。有潭颇广。而水色不甚澄澈。四顾峰壁环合。有一岩特立如手掌。高可数十丈。腰以上不附于山。正临潭上甚奇。号为明镜台。潭右有大石可坐。石面。刻玉镜潭三字。潭左垒石为小城。城有门。僧辈号为地狱门。入城沿溪。行百馀步。转出明镜台后面。左右岩峦。愈出愈奇。溪回路转。若不可穷闻。更入五里许。有现佛庵。号为幽胜。而倦甚不能进。复循溪而出。渡万瀑下流。行千馀步。有一巨潭。汇石中深不可测。水色沉黑可畏。所谓鸣韵潭也。潭左苍壁。削立数十丈。潭上石势盘陀。溪水逶迤而下。泻入潭中。路由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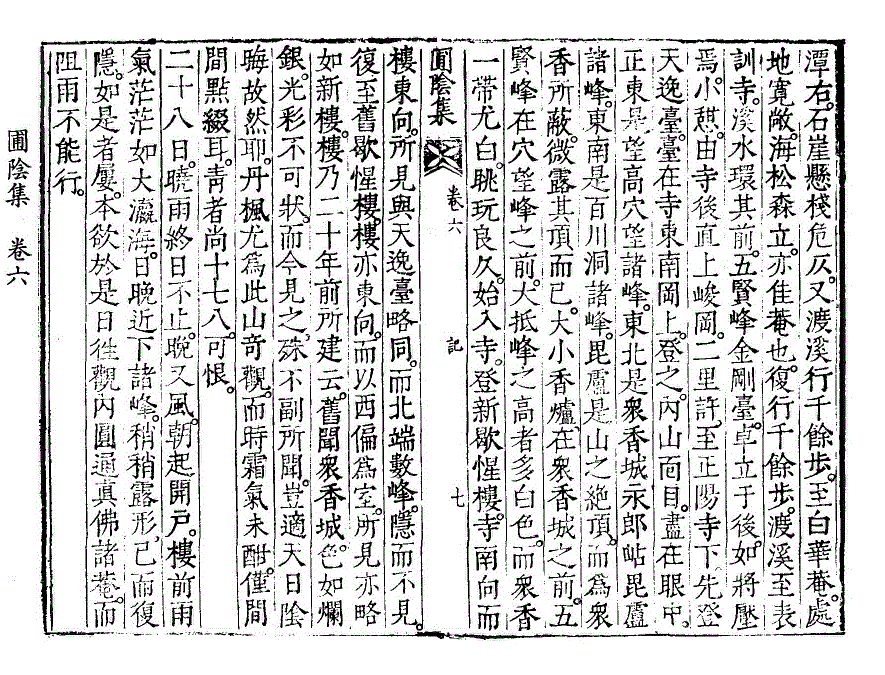 潭右。石崖悬栈危仄。又渡溪行千馀步。至白华庵。处地宽敞。海松森立。亦佳庵也。复行千馀步。渡溪至表训寺。溪水环其前。五贤峰金刚台。卓立于后。如将压焉。小憩。由寺后直上峻冈。二里许。至正阳寺下。先登天逸台。台在寺东南冈上。登之。内山面目。尽在眼中。正东是望高穴望诸峰。东北是众香城永郎岾毗卢诸峰。东南是百川洞诸峰。毗卢是山之绝顶。而为众香所蔽。微露其顶而已。大小香炉。在众香城之前。五贤峰在穴望峰之前。大抵峰之高者多白色。而众香一带尤白。眺玩良久。始入寺。登新歇惺楼。寺南向而楼东向。所见与天逸台略同。而北端数峰。隐而不见。复至旧歇惺楼。楼亦东向。而以西偏为室。所见亦略如新楼。楼乃二十年前所建云。旧闻众香城。色如烂银。光彩不可状。而今见之。殊不副所闻。岂适天日阴晦故然耶。丹枫尤为此山奇观。而时霜气未酣。仅间间点缀耳。青者尚十七八。可恨。
潭右。石崖悬栈危仄。又渡溪行千馀步。至白华庵。处地宽敞。海松森立。亦佳庵也。复行千馀步。渡溪至表训寺。溪水环其前。五贤峰金刚台。卓立于后。如将压焉。小憩。由寺后直上峻冈。二里许。至正阳寺下。先登天逸台。台在寺东南冈上。登之。内山面目。尽在眼中。正东是望高穴望诸峰。东北是众香城永郎岾毗卢诸峰。东南是百川洞诸峰。毗卢是山之绝顶。而为众香所蔽。微露其顶而已。大小香炉。在众香城之前。五贤峰在穴望峰之前。大抵峰之高者多白色。而众香一带尤白。眺玩良久。始入寺。登新歇惺楼。寺南向而楼东向。所见与天逸台略同。而北端数峰。隐而不见。复至旧歇惺楼。楼亦东向。而以西偏为室。所见亦略如新楼。楼乃二十年前所建云。旧闻众香城。色如烂银。光彩不可状。而今见之。殊不副所闻。岂适天日阴晦故然耶。丹枫尤为此山奇观。而时霜气未酣。仅间间点缀耳。青者尚十七八。可恨。二十八日。晓雨终日不止。晚又风。朝起开户。楼前雨气茫茫如大瀛海。日晚近下诸峰。稍稍露形。已而复隐。如是者屡。本欲于是日往观内圆通真佛诸庵。而阻雨不能行。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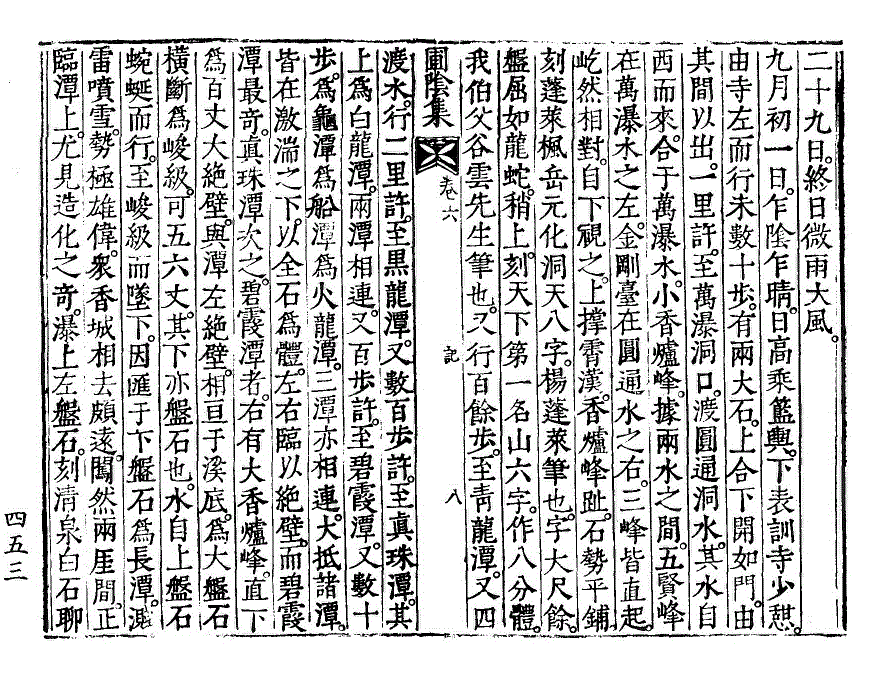 二十九日。终日微雨大风。
二十九日。终日微雨大风。壬辰九月
九月初一日。乍阴乍晴。日高乘篮舆。下表训寺少憩。由寺左而行未数十步。有两大石。上合下开如门。由其间以出。一里许。至万瀑洞口。渡圆通洞水。其水自西而来。合于万瀑水。小香炉峰。据两水之间。五贤峰在万瀑水之左。金刚台在圆通水之右。三峰皆直起。屹然相对。自下视之。上撑霄汉。香炉峰趾。石势平铺。刻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八字。杨蓬莱笔也。字大尺馀。盘屈如龙蛇。稍上。刻天下第一名山六字。作八分体。我伯父谷云先生笔也。又行百馀步。至青龙潭。又四渡水。行二里许。至黑龙潭。又数百步许。至真珠潭。其上为白龙潭。两潭相连。又百步许。至碧霞潭。又数十步。为龟潭为船潭为火龙潭。三潭亦相连。大抵诸潭。皆在激湍之下。以全石为体。左右临以绝壁。而碧霞潭最奇。真珠潭次之。碧霞潭者。右有大香炉峰。直下为百丈大绝壁。与潭左绝壁。相亘于溪底。为大盘石横断为峻级。可五六丈。其下亦盘石也。水自上盘石蜿蜒而行。至峻级而坠下。因汇于下盘石为长潭。溅雷喷雪。势极雄伟。众香城相去颇远。闯然两厓间。正临潭上。尤见造化之奇。瀑上左盘石。刻清泉白石聊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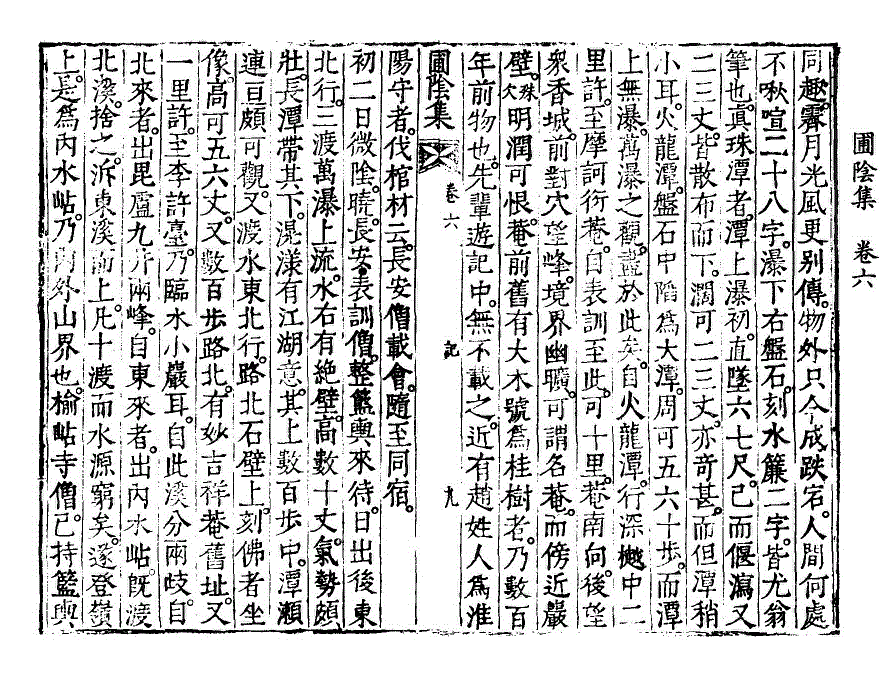 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物外只今成跌宕。人间何处不啾喧二十八字。瀑下右盘石。刻水帘二字。皆尤翁笔也。真珠潭者。潭上瀑初。直坠六七尺。已而偃泻又二三丈。皆散布而下。阔可二三丈。亦奇甚。而但潭稍小耳。火龙潭。盘石中陷为大潭。周可五六十步。而潭上无瀑。万瀑之观。尽于此矣。自火龙潭。行深樾中二里许。至摩诃衍庵。自表训至此。可十里。庵南向。后望众香城。前对穴望峰。境界幽旷。可谓名庵。而傍近岩壁。(殊欠)明润可恨。庵前旧有大木号为桂树者。乃数百年前物也。先辈游记中。无不载之。近有赵姓人为淮阳守者。伐棺材云。长安僧载会。随至同宿。
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物外只今成跌宕。人间何处不啾喧二十八字。瀑下右盘石。刻水帘二字。皆尤翁笔也。真珠潭者。潭上瀑初。直坠六七尺。已而偃泻又二三丈。皆散布而下。阔可二三丈。亦奇甚。而但潭稍小耳。火龙潭。盘石中陷为大潭。周可五六十步。而潭上无瀑。万瀑之观。尽于此矣。自火龙潭。行深樾中二里许。至摩诃衍庵。自表训至此。可十里。庵南向。后望众香城。前对穴望峰。境界幽旷。可谓名庵。而傍近岩壁。(殊欠)明润可恨。庵前旧有大木号为桂树者。乃数百年前物也。先辈游记中。无不载之。近有赵姓人为淮阳守者。伐棺材云。长安僧载会。随至同宿。初二日微阴。晓。长安,表训僧。整篮舆来待。日出后东北行。三渡万瀑上流。水右有绝壁。高数十丈。气势颇壮。长潭带其下。滉漾有江湖意。其上数百步中。潭濑连亘颇可观。又渡水东北行。路北石壁上。刻佛者坐像。高可五六丈。又数百步路北。有妙吉祥庵旧址。又一里许。至李许台。乃临水小岩耳。自此溪分两歧。自北来者。出毗卢九井两峰。自东来者。出内水岾。既渡北溪。舍之。溯东溪而上。凡十渡而水源穷矣。遂登岭上。是为内水岾。乃内外山界也。榆岾寺僧。已持篮舆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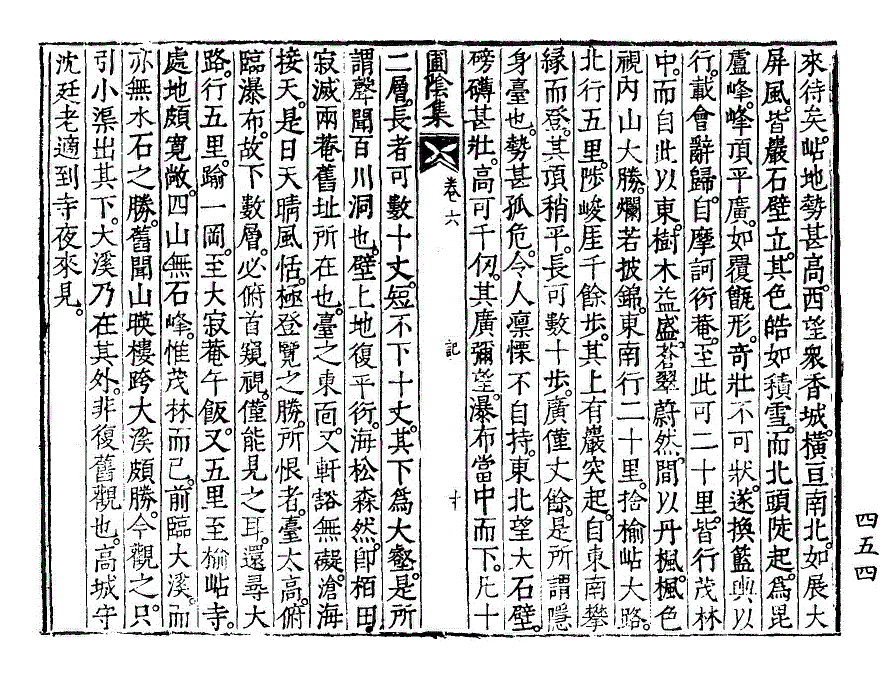 来待矣。岾地势甚高。西望众香城。横亘南北。如展大屏风。皆岩石壁立。其色皓如积雪。而北头陡起。为毗卢峰。峰顶平广。如覆甑形。奇壮不可状。遂换篮舆以行。载会辞归。自摩诃衍庵。至此可二十里。皆行茂林中。而自此以东。树木益盛。苍翠蔚然。间以丹枫。枫色视内山大胜。烂若披锦。东南行二十里。舍榆岾大路。北行五里。陟峻厓千馀步。其上有岩突起。自东南攀缘而登。其顶稍平。长可数十步。广仅丈馀。是所谓隐身台也。势甚孤危。令人凛慄不自持。东北望大石壁。磅礴甚壮。高可千仞。其广弥望。瀑布当中而下。凡十二层。长者可数十丈。短不下十丈。其下为大壑。是所谓声闻百川洞也。壁上地复平衍。海松森然。即柏田,寂灭两庵旧址所在也。台之东面。又轩豁无碍。沧海接天。是日天晴风恬。极登览之胜。所恨者。台太高。俯临瀑布。故下数层。必俯首窥视。仅能见之耳。还寻大路。行五里。踰一冈。至大寂庵午饭。又五里至榆岾寺。处地颇宽敞。四山无石峰。惟茂林而已。前临大溪。而亦无水石之胜。旧闻山映楼跨大溪颇胜。今观之。只引小渠出其下。大溪乃在其外。非复旧观也。高城守沈廷老适到寺夜来见。
来待矣。岾地势甚高。西望众香城。横亘南北。如展大屏风。皆岩石壁立。其色皓如积雪。而北头陡起。为毗卢峰。峰顶平广。如覆甑形。奇壮不可状。遂换篮舆以行。载会辞归。自摩诃衍庵。至此可二十里。皆行茂林中。而自此以东。树木益盛。苍翠蔚然。间以丹枫。枫色视内山大胜。烂若披锦。东南行二十里。舍榆岾大路。北行五里。陟峻厓千馀步。其上有岩突起。自东南攀缘而登。其顶稍平。长可数十步。广仅丈馀。是所谓隐身台也。势甚孤危。令人凛慄不自持。东北望大石壁。磅礴甚壮。高可千仞。其广弥望。瀑布当中而下。凡十二层。长者可数十丈。短不下十丈。其下为大壑。是所谓声闻百川洞也。壁上地复平衍。海松森然。即柏田,寂灭两庵旧址所在也。台之东面。又轩豁无碍。沧海接天。是日天晴风恬。极登览之胜。所恨者。台太高。俯临瀑布。故下数层。必俯首窥视。仅能见之耳。还寻大路。行五里。踰一冈。至大寂庵午饭。又五里至榆岾寺。处地颇宽敞。四山无石峰。惟茂林而已。前临大溪。而亦无水石之胜。旧闻山映楼跨大溪颇胜。今观之。只引小渠出其下。大溪乃在其外。非复旧观也。高城守沈廷老适到寺夜来见。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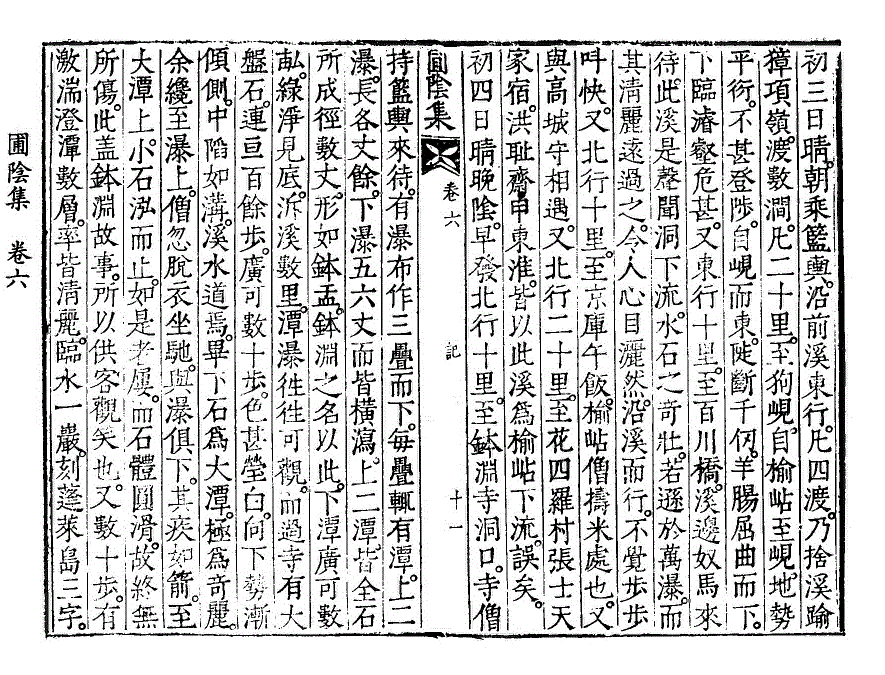 初三日晴。朝乘篮舆。沿前溪东行。凡四渡。乃舍溪踰獐项岭。渡数涧。凡二十里。至狗岘。自榆岾至岘。地势平衍。不甚登陟。自岘而东。陡断千仞。羊肠屈曲而下。下临浚壑危甚。又东行十里。至百川桥。溪边奴马来待。此溪是声闻洞下流。水石之奇壮。若逊于万瀑。而其清丽远过之。令人心目洒然。沿溪而行。不觉步步叫快。又北行十里。至京库午饭。榆岾僧捣米处也。又与高城守相遇。又北行二十里。至花四罗村张士天家宿。洪耻斋,申东淮。皆以此溪为榆岾下流。误矣。
初三日晴。朝乘篮舆。沿前溪东行。凡四渡。乃舍溪踰獐项岭。渡数涧。凡二十里。至狗岘。自榆岾至岘。地势平衍。不甚登陟。自岘而东。陡断千仞。羊肠屈曲而下。下临浚壑危甚。又东行十里。至百川桥。溪边奴马来待。此溪是声闻洞下流。水石之奇壮。若逊于万瀑。而其清丽远过之。令人心目洒然。沿溪而行。不觉步步叫快。又北行十里。至京库午饭。榆岾僧捣米处也。又与高城守相遇。又北行二十里。至花四罗村张士天家宿。洪耻斋,申东淮。皆以此溪为榆岾下流。误矣。初四日晴晚阴。早发北行十里。至钵渊寺洞口。寺僧持篮舆来待。有瀑布作三叠而下。每叠辄有潭。上二瀑。长各丈馀。下瀑五六丈而皆横泻。上二潭。皆全石所成径数丈。形如钵盂。钵渊之名以此。下潭广可数亩。绿净见底。溯溪数里。潭瀑往往可观。而过寺有大盘石。连亘百馀步。广可数十步。色甚莹白。向下势渐倾侧。中陷如沟。溪水道焉。毕下石为大潭。极为奇丽。余才至瀑上。僧忽脱衣坐驰。与瀑俱下。其疾如箭。至大潭上。小石泓而止。如是者屡。而石体圆滑。故终无所伤。此盖钵渊故事。所以供客观笑也。又数十步。有激湍澄潭数层。率皆清丽。临水一岩。刻蓬莱岛三字。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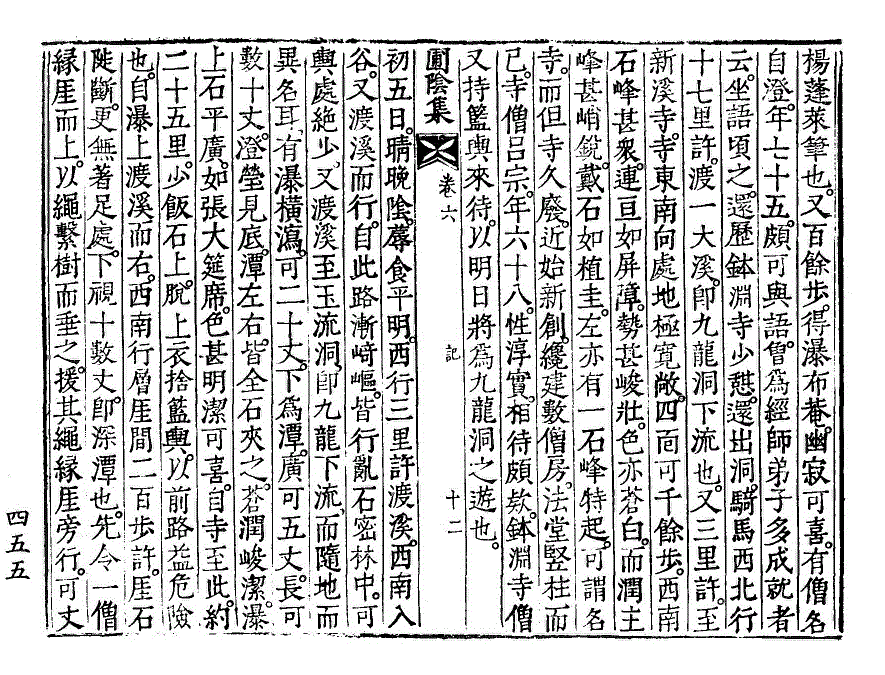 杨蓬莱笔也。又百馀步。得瀑布庵。幽寂可喜。有僧名自澄。年七十五。颇可与语。曾为经师弟子多成就者云。坐语顷之。还历钵渊寺少憩。还出洞。骑马西北行十七里许。渡一大溪。即九龙洞下流也。又三里许。至新溪寺。寺东南向处地极宽敞。四面可千馀步。西南石峰甚众。连亘如屏障。势甚峻壮。色亦苍白。而润主峰甚峭锐。戴石如植圭。左亦有一石峰特起。可谓名寺。而但寺久废。近始新创。才建数僧房。法堂竖柱而已。寺僧吕宗。年六十八。性淳实。相待颇款。钵渊寺僧又持篮舆来待。以明日将为九龙洞之游也。
杨蓬莱笔也。又百馀步。得瀑布庵。幽寂可喜。有僧名自澄。年七十五。颇可与语。曾为经师弟子多成就者云。坐语顷之。还历钵渊寺少憩。还出洞。骑马西北行十七里许。渡一大溪。即九龙洞下流也。又三里许。至新溪寺。寺东南向处地极宽敞。四面可千馀步。西南石峰甚众。连亘如屏障。势甚峻壮。色亦苍白。而润主峰甚峭锐。戴石如植圭。左亦有一石峰特起。可谓名寺。而但寺久废。近始新创。才建数僧房。法堂竖柱而已。寺僧吕宗。年六十八。性淳实。相待颇款。钵渊寺僧又持篮舆来待。以明日将为九龙洞之游也。初五日。晴晚阴。蓐食平明。西行三里许渡溪。西南入谷。又渡溪而行。自此路渐崎岖。皆行乱石密林中。可舆处绝少。又渡溪至玉流洞。即九龙下流。而随地而异名耳。有瀑横泻。可二十丈。下为潭。广可五丈。长可数十丈。澄莹见底。潭左右。皆全石夹之。苍润峻洁。瀑上石平广。如张大筵席。色甚明洁可喜。自寺至此。约二十五里。少饭石上。脱上衣舍篮舆。以前路益危险也。自瀑上渡溪而右。西南行层厓间二百步许。厓石陡断。更无著足处。下视十数丈。即深潭也。先令一僧缘厓而上。以绳系树而垂之。援其绳缘厓旁行。可丈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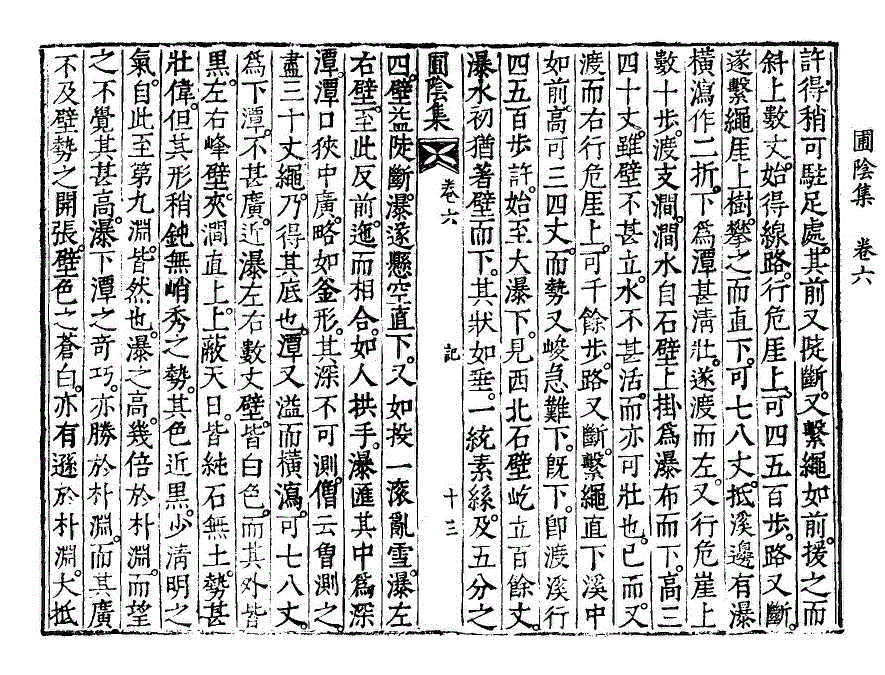 许得稍可驻足处。其前又陡断。又系绳如前。援之而斜上数丈。始得线路。行危厓上。可四五百步。路又断。遂系绳厓上树。攀之而直下。可七八丈。抵溪边有瀑横泻作二折。下为潭甚清壮。遂渡而左。又行危崖上数十步。渡支涧。涧水自石壁上挂为瀑布而下。高三四十丈。虽壁不甚立。水不甚活。而亦可壮也。已而。又渡而右行危厓上。可千馀步。路又断。系绳直下溪中如前。高可三四丈。而势又峻急难下。既下。即渡溪行四五百步许。始至大瀑下。见西北石壁屹立百馀丈。瀑水初犹著壁而下。其状如垂。一统素丝。及五分之四。壁益陡断。瀑遂悬空直下。又如投一滚乱雪。瀑左右壁。至此反前。迤而相合。如人拱手。瀑汇其中为深潭。潭口狭中广。略如釜形。其深不可测。僧云曾测之。尽三十丈绳。乃得其底也。潭又溢而横泻。可七八丈。为下潭。不甚广。近瀑左右数丈壁。皆白色。而其外皆黑。左右峰壁。夹涧直上。上蔽天日。皆纯石无土。势甚壮伟。但其形稍钝无峭秀之势。其色近黑。少清明之气。自此至第九渊。皆然也。瀑之高。几倍于朴渊。而望之不觉其甚高。瀑下潭之奇巧。亦胜于朴渊。而其广不及壁势之开张。壁色之苍白。亦有逊于朴渊。大抵
许得稍可驻足处。其前又陡断。又系绳如前。援之而斜上数丈。始得线路。行危厓上。可四五百步。路又断。遂系绳厓上树。攀之而直下。可七八丈。抵溪边有瀑横泻作二折。下为潭甚清壮。遂渡而左。又行危崖上数十步。渡支涧。涧水自石壁上挂为瀑布而下。高三四十丈。虽壁不甚立。水不甚活。而亦可壮也。已而。又渡而右行危厓上。可千馀步。路又断。系绳直下溪中如前。高可三四丈。而势又峻急难下。既下。即渡溪行四五百步许。始至大瀑下。见西北石壁屹立百馀丈。瀑水初犹著壁而下。其状如垂。一统素丝。及五分之四。壁益陡断。瀑遂悬空直下。又如投一滚乱雪。瀑左右壁。至此反前。迤而相合。如人拱手。瀑汇其中为深潭。潭口狭中广。略如釜形。其深不可测。僧云曾测之。尽三十丈绳。乃得其底也。潭又溢而横泻。可七八丈。为下潭。不甚广。近瀑左右数丈壁。皆白色。而其外皆黑。左右峰壁。夹涧直上。上蔽天日。皆纯石无土。势甚壮伟。但其形稍钝无峭秀之势。其色近黑。少清明之气。自此至第九渊。皆然也。瀑之高。几倍于朴渊。而望之不觉其甚高。瀑下潭之奇巧。亦胜于朴渊。而其广不及壁势之开张。壁色之苍白。亦有逊于朴渊。大抵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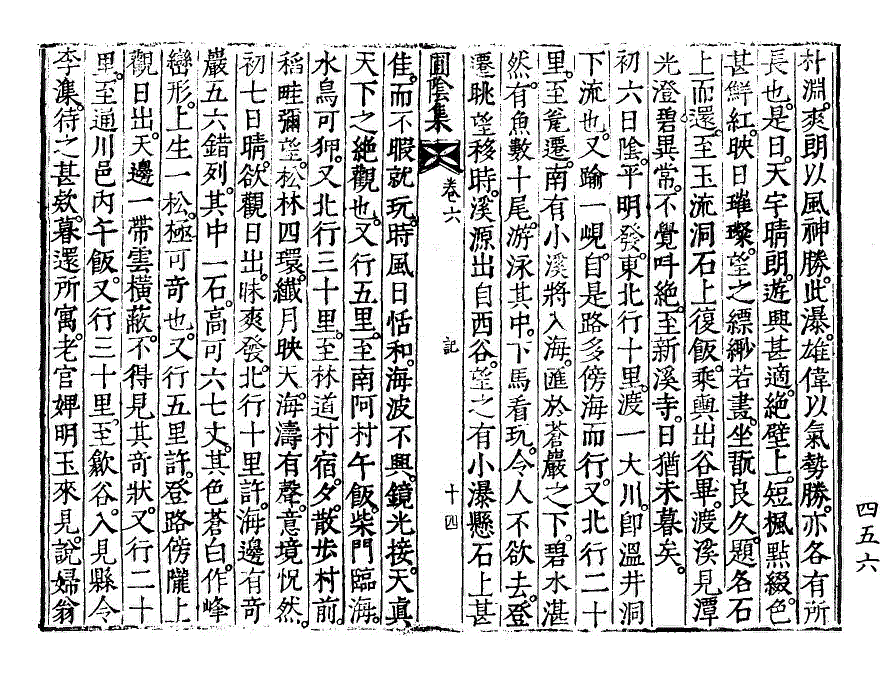 朴渊。爽朗以风神胜。此瀑。雄伟以气势胜。亦各有所长也。是日。天宇晴朗。游兴甚适。绝壁上。短枫点缀。色甚鲜红。映日璀璨。望之缥缈若画。坐玩良久。题名石上而还。至玉流洞石上复饭。乘舆出谷毕。渡溪见潭光澄碧异常。不觉叫绝。至新溪寺。日犹未暮矣。
朴渊。爽朗以风神胜。此瀑。雄伟以气势胜。亦各有所长也。是日。天宇晴朗。游兴甚适。绝壁上。短枫点缀。色甚鲜红。映日璀璨。望之缥缈若画。坐玩良久。题名石上而还。至玉流洞石上复饭。乘舆出谷毕。渡溪见潭光澄碧异常。不觉叫绝。至新溪寺。日犹未暮矣。初六日阴。平明发。东北行十里。渡一大川。即温井洞下流也。又踰一岘。自是路多傍海而行。又北行二十里。至瓮迁。南有小溪将入海。汇于苍岩之下。碧水湛然。有鱼数十尾。游泳其中。下马看玩。令人不欲去。登迁眺望移时。溪源出自西谷。望之有小瀑悬石上甚佳。而不暇就玩。时风日恬和。海波不兴。镜光接天。真天下之绝观也。又行五里。至南阿村午饭。柴门临海。水鸟可狎。又北行三十里。至林道村宿。夕。散步村前。稻畦弥望。松林四环。纤月映天。海涛有声。意境恍然。
初七日晴。欲观日出。昧爽发。北行十里许。海边有奇岩五六错列。其中一石。高可六七丈。其色苍白。作峰峦形。上生一松。极可奇也。又行五里许。登路傍陇上观日出。天边一带云横蔽。不得见其奇状。又行二十里。至通川邑内午饭。又行三十里。至歙谷。入见县令李潗。待之甚款。暮还所寓。老官婢明玉来见。说妇翁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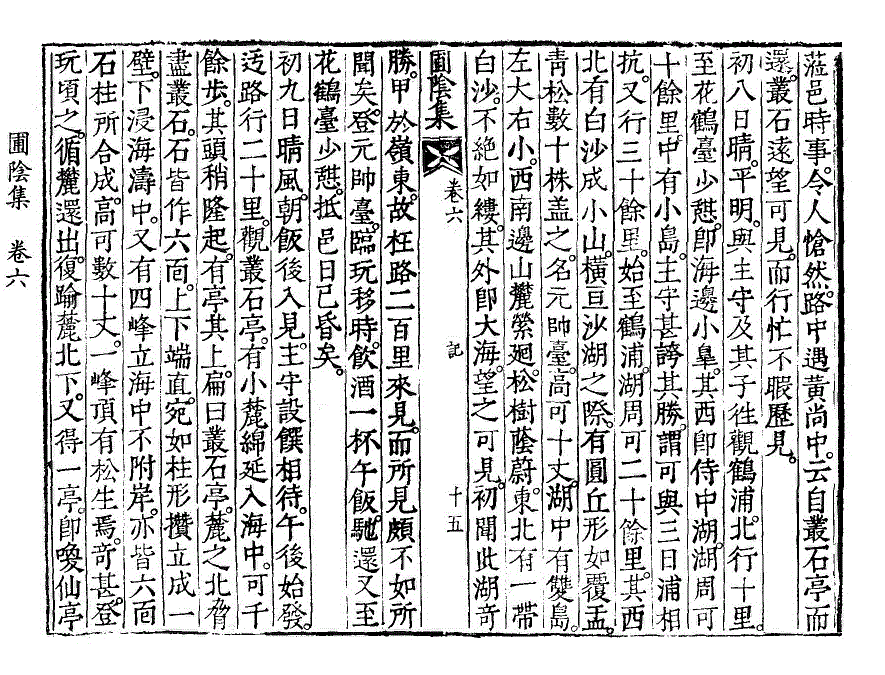 莅邑时事。令人怆然。路中遇黄尚中。云自丛石亭而还。丛石远望可见。而行忙不暇历见。
莅邑时事。令人怆然。路中遇黄尚中。云自丛石亭而还。丛石远望可见。而行忙不暇历见。初八日晴。平明。与主守及其子往观鹤浦。北行十里。至花鹤台少憩。即海边小皋。其西即侍中湖。湖周可十馀里。中有小岛。主守甚誇其胜。谓可与三日浦相抗。又行三十馀里。始至鹤浦。湖周可二十馀里。其西北有白沙成小山。横亘沙湖之际。有圆丘形如覆盂。青松数十株盖之。名元帅台。高可十丈。湖中有双岛。左大右小。西南边山麓萦回。松树荫蔚。东北有一带白沙。不绝如缕。其外即大海。望之可见。初闻此湖奇胜。甲于岭东。故枉路二百里来见。而所见颇不如所闻矣。登元帅台。临玩移时。饮酒一杯午饭。驰还又至花鹤台少憩。抵邑日已昏矣。
初九日晴风。朝饭后入见。主守设馔相待。午后始发。迂路行二十里。观丛石亭。有小麓绵延入海中。可千馀步。其头稍隆起。有亭其上。扁曰丛石亭。麓之北胁尽丛石。石皆作六面。上下端直。宛如柱形攒立成一壁。下浸海涛中。又有四峰立海中不附岸。亦皆六面石柱所合成。高可数十丈。一峰顶有松生焉。奇甚。登玩顷之。循麓还出。复踰麓北下。又得一亭。即唤仙亭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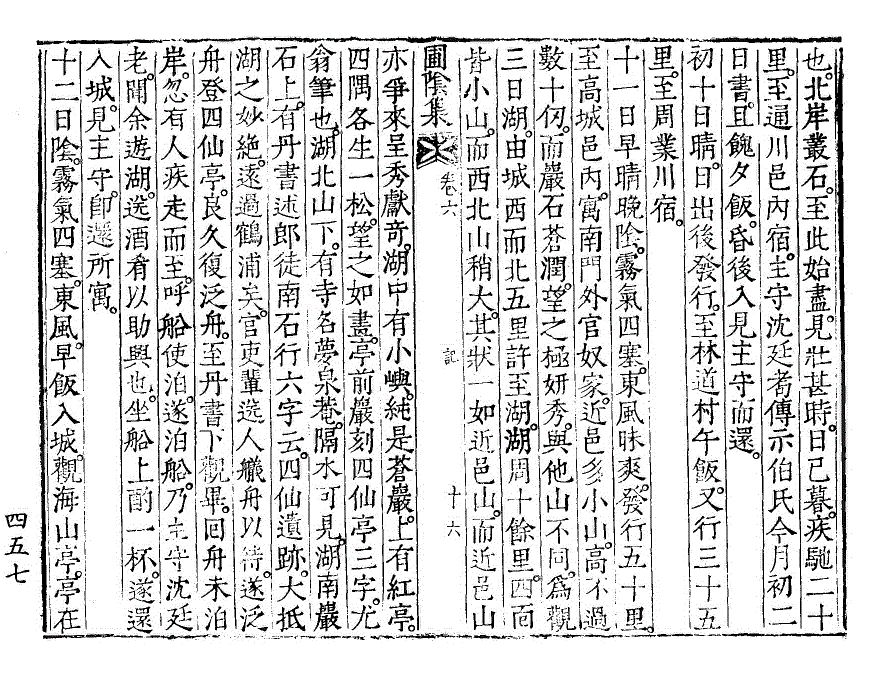 也。北岸丛石。至此始尽。见壮甚时。日已暮。疾驰二十里。至通川邑内宿。主守沈廷耇传示伯氏今月初二日书。且馈夕饭。昏后入见主守而还。
也。北岸丛石。至此始尽。见壮甚时。日已暮。疾驰二十里。至通川邑内宿。主守沈廷耇传示伯氏今月初二日书。且馈夕饭。昏后入见主守而还。初十日晴。日出后发行。至林道村午饭。又行三十五里。至周业川宿。
十一日早晴晚阴。雾气四塞。东风昧爽。发行五十里。至高城邑内。寓南门外官奴家。近邑多小山。高不过数十仞。而岩石苍润。望之极妍秀。与他山不同。为观三日湖。由城西而北五里许至湖。湖周十馀里。四面皆小山。而西北山稍大。其状一如近邑山。而近邑山亦争来呈秀献奇。湖中有小屿。纯是苍岩。上有红亭。四隅各生一松。望之如画。亭前岩刻四仙亭三字。尤翁笔也。湖北山下。有寺名梦泉庵。隔水可见。湖南岩石上。有丹书述郎徒南石行六字云。四仙遗迹。大抵湖之妙绝。远过鹤浦矣。官吏辈送人舣舟以待。遂泛舟登四仙亭。良久复泛舟。至丹书下观毕。回舟未泊岸。忽有人疾走而至。呼船使泊。遂泊船。乃主守沈廷老。闻余游湖。送酒肴以助兴也。坐船上酌一杯。遂还入城。见主守。即还所寓。
十二日阴。雾气四塞。东风。早饭入城。观海山亭。亭在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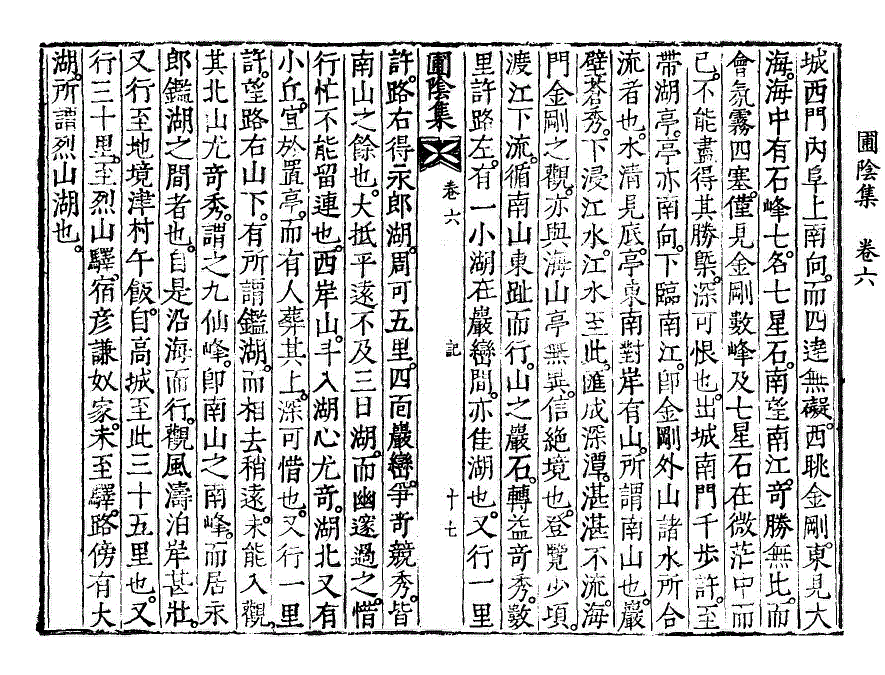 城西门内阜上南向。而四达无碍。西眺金刚。东见大海。海中有石峰七。名七星石。南望南江。奇胜无比。而会氛雾四塞。仅见金刚数峰及七星石在微茫中而已。不能尽得其胜槩。深可恨也。出城南门千步许。至带湖亭。亭亦南向。下临南江。即金刚外山诸水所合流者也。水清见底。亭东南对岸有山。所谓南山也。岩壁苍秀。下浸江水。江水至此。汇成深潭。湛湛不流。海门金刚之观。亦与海山亭无异。信绝境也。登览少顷。渡江下流。循南山东趾而行。山之岩石。转益奇秀。数里许路左。有一小湖在岩峦间。亦佳湖也。又行一里许。路右得永郎湖。周可五里。四面岩峦。争奇竞秀。皆南山之馀也。大抵平远不及三日湖。而幽邃过之。惜行忙不能留连也。西岸山。斗入湖心尤奇。湖北又有小丘。宜于置亭。而有人葬其上。深可惜也。又行一里许。望路右山下。有所谓鉴湖。而相去稍远。未能入观。其北山尤奇秀。谓之九仙峰。即南山之南峰。而居永郎鉴湖之间者也。自是沿海而行。观风涛泊岸甚壮。又行至地境津村午饭。自高城至此三十五里也。又行三十里。至烈山驿。宿彦谦奴家。未至驿。路傍有大湖。所谓烈山湖也。
城西门内阜上南向。而四达无碍。西眺金刚。东见大海。海中有石峰七。名七星石。南望南江。奇胜无比。而会氛雾四塞。仅见金刚数峰及七星石在微茫中而已。不能尽得其胜槩。深可恨也。出城南门千步许。至带湖亭。亭亦南向。下临南江。即金刚外山诸水所合流者也。水清见底。亭东南对岸有山。所谓南山也。岩壁苍秀。下浸江水。江水至此。汇成深潭。湛湛不流。海门金刚之观。亦与海山亭无异。信绝境也。登览少顷。渡江下流。循南山东趾而行。山之岩石。转益奇秀。数里许路左。有一小湖在岩峦间。亦佳湖也。又行一里许。路右得永郎湖。周可五里。四面岩峦。争奇竞秀。皆南山之馀也。大抵平远不及三日湖。而幽邃过之。惜行忙不能留连也。西岸山。斗入湖心尤奇。湖北又有小丘。宜于置亭。而有人葬其上。深可惜也。又行一里许。望路右山下。有所谓鉴湖。而相去稍远。未能入观。其北山尤奇秀。谓之九仙峰。即南山之南峰。而居永郎鉴湖之间者也。自是沿海而行。观风涛泊岸甚壮。又行至地境津村午饭。自高城至此三十五里也。又行三十里。至烈山驿。宿彦谦奴家。未至驿。路傍有大湖。所谓烈山湖也。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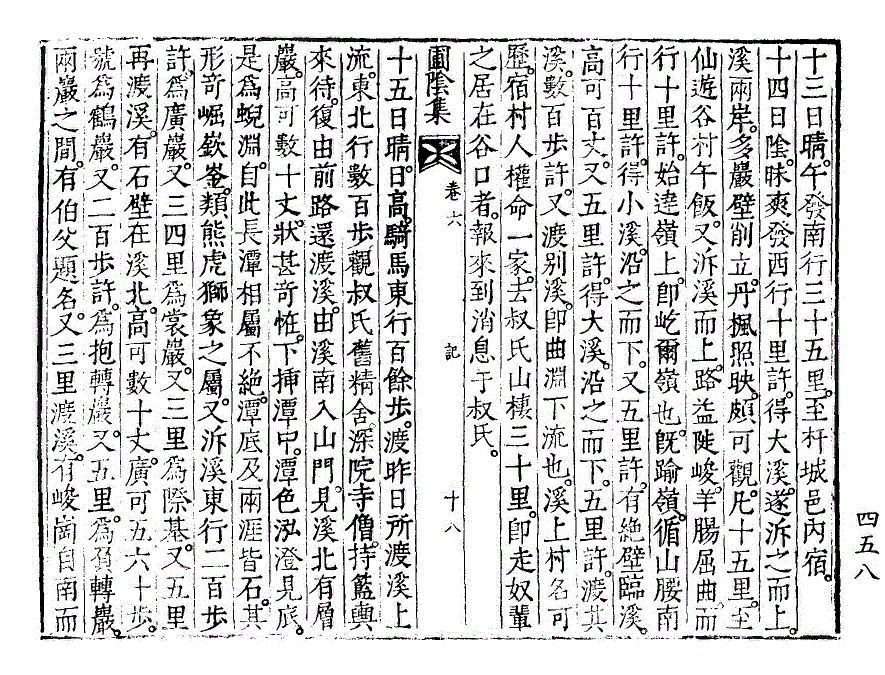 十三日晴。午发南行三十五里。至杆城邑内宿。
十三日晴。午发南行三十五里。至杆城邑内宿。十四日阴。昧爽发西行十里许。得大溪。遂溯之而上。溪两岸。多岩壁削立。丹枫照映。颇可观。凡十五里。至仙游谷村午饭。又溯溪而上。路益陡峻。羊肠屈曲。而行十里许。始达岭上。即屹尔岭也。既踰岭。循山腰南行十里许。得小溪。沿之而下。又五里许。有绝壁临溪。高可百丈。又五里许。得大溪。沿之而下。五里许。渡其溪。数百步许。又渡别溪。即曲渊下流也。溪上村名可历。宿村人权命一家。去叔氏山栖三十里。即走奴辈之居在谷口者。报来到消息于叔氏。
十五日晴。日高。骑马东行百馀步。渡昨日所渡溪上流。东北行数百步。观叔氏旧精舍。深院寺僧。持篮舆来待。复由前路还渡溪。由溪南入山门。见溪北有层岩。高可数十丈。状甚奇怪。下插潭中。潭色泓澄见底。是为蜺渊。自此长潭相属不绝。潭底及两涯皆石。其形奇崛嵚崟。类熊虎狮象之属。又溯溪东行二百步许。为广岩。又三四里为裳岩。又三里为际基。又五里再渡溪。有石壁在溪北。高可数十丈。广可五六十步。号为鹤岩。又二百步许。为抱转岩。又五里。为负转岩。两岩之间。有伯父题名。又三里渡溪。有峻岗自南而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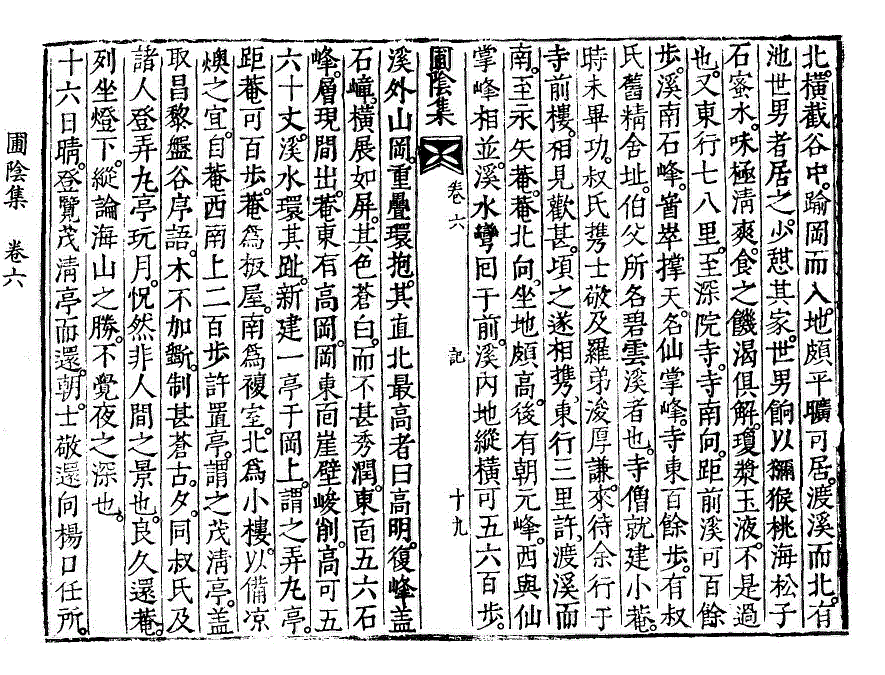 北。横截谷中。踰冈而入。地颇平旷可居。渡溪而北。有池世男者居之。少憩其家。世男饷以猕猴桃海松子石蜜水。味极清爽。食之饥渴俱解。琼浆玉液。不是过也。又东行七八里。至深院寺。寺南向。距前溪可百馀步。溪南石峰。𡺚崒撑天。名仙掌峰。寺东百馀步。有叔氏旧精舍址。伯父所名碧云溪者也。寺僧就建小庵。时未毕功。叔氏携士敬及罗弟浚厚谦。来待余行于寺前楼。相见欢甚。顷之遂相携。东行三里许。渡溪而南。至永矢庵。庵北向。坐地颇高。后有朝元峰。西与仙掌峰相并。溪水弯回于前。溪内地纵横可五六百步。溪外山冈。重叠环抱。其直北最高者曰高明。复峰盖石嶂。横展如屏。其色苍白。而不甚秀润。东面五六石峰。层现间出。庵东有高冈。冈东面崖壁峻削。高可五六十丈。溪水环其趾。新建一亭于冈上。谓之弄丸亭。距庵可百步。庵为板屋。南为复室。北为小楼。以备凉燠之宜。自庵西南上二百步许置亭。谓之茂清亭。盖取昌黎盘谷序语。木不加斲。制甚苍古。夕。同叔氏及诸人登弄丸亭玩月。恍然非人间之景也。良久还庵。列坐灯下。纵论海山之胜。不觉夜之深也。
北。横截谷中。踰冈而入。地颇平旷可居。渡溪而北。有池世男者居之。少憩其家。世男饷以猕猴桃海松子石蜜水。味极清爽。食之饥渴俱解。琼浆玉液。不是过也。又东行七八里。至深院寺。寺南向。距前溪可百馀步。溪南石峰。𡺚崒撑天。名仙掌峰。寺东百馀步。有叔氏旧精舍址。伯父所名碧云溪者也。寺僧就建小庵。时未毕功。叔氏携士敬及罗弟浚厚谦。来待余行于寺前楼。相见欢甚。顷之遂相携。东行三里许。渡溪而南。至永矢庵。庵北向。坐地颇高。后有朝元峰。西与仙掌峰相并。溪水弯回于前。溪内地纵横可五六百步。溪外山冈。重叠环抱。其直北最高者曰高明。复峰盖石嶂。横展如屏。其色苍白。而不甚秀润。东面五六石峰。层现间出。庵东有高冈。冈东面崖壁峻削。高可五六十丈。溪水环其趾。新建一亭于冈上。谓之弄丸亭。距庵可百步。庵为板屋。南为复室。北为小楼。以备凉燠之宜。自庵西南上二百步许置亭。谓之茂清亭。盖取昌黎盘谷序语。木不加斲。制甚苍古。夕。同叔氏及诸人登弄丸亭玩月。恍然非人间之景也。良久还庵。列坐灯下。纵论海山之胜。不觉夜之深也。十六日晴。登览茂清亭而还。朝。士敬还向杨口任所。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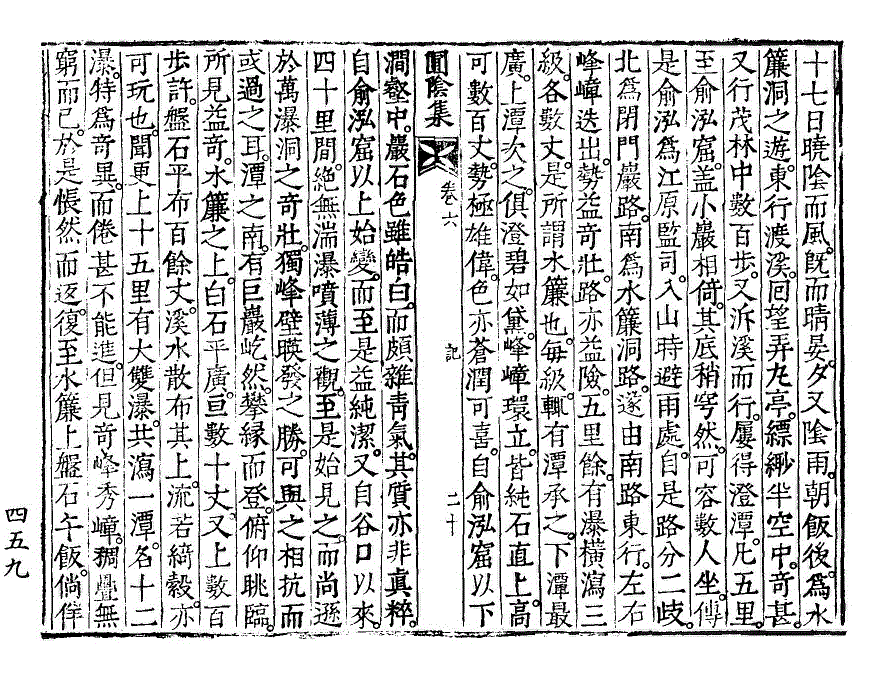 十七日晓阴而风。既而晴晏。夕又阴雨。朝饭后。为水帘洞之游。东行渡溪。回望弄丸亭。缥缈半空中。奇甚。又行茂林中数百步。又溯溪而行。屡得澄潭。凡五里。至俞泓窟。盖小岩相倚。其底稍穹然。可容数人坐。传是俞泓为江原监司。入山时避雨处。自是路分二歧。北为闭门岩路。南为水帘洞路。遂由南路东行。左右峰嶂迭出。势益奇壮。路亦益险。五里馀。有瀑横泻三级。各数丈。是所谓水帘也。每级。辄有潭承之。下潭最广。上潭次之。俱澄碧如黛。峰嶂环立。皆纯石直上。高可数百丈。势极雄伟。色亦苍润可喜。自俞泓窟以下涧壑中。岩石色虽皓白。而颇杂青气。其质亦非真粹。自俞泓窟以上始变。而至是益纯洁。又自谷口以来。四十里间。绝无湍瀑喷薄之观。至是始见之。而尚逊于万瀑洞之奇壮。独峰壁映发之胜。可与之相抗而或过之耳。潭之南。有巨岩屹然。攀缘而登。俯仰眺临。所见益奇。水帘之上。白石平广。亘数十丈。又上数百步许。盘石平布百馀丈。溪水散布其上。流若绮縠。亦可玩也。闻更上十五里有大双瀑。共泻一潭。名十二瀑。特为奇异。而倦甚不能进。但见奇峰秀嶂。稠叠无穷而已。于是怅然而返。复至水帘上盘石午饭。倘佯
十七日晓阴而风。既而晴晏。夕又阴雨。朝饭后。为水帘洞之游。东行渡溪。回望弄丸亭。缥缈半空中。奇甚。又行茂林中数百步。又溯溪而行。屡得澄潭。凡五里。至俞泓窟。盖小岩相倚。其底稍穹然。可容数人坐。传是俞泓为江原监司。入山时避雨处。自是路分二歧。北为闭门岩路。南为水帘洞路。遂由南路东行。左右峰嶂迭出。势益奇壮。路亦益险。五里馀。有瀑横泻三级。各数丈。是所谓水帘也。每级。辄有潭承之。下潭最广。上潭次之。俱澄碧如黛。峰嶂环立。皆纯石直上。高可数百丈。势极雄伟。色亦苍润可喜。自俞泓窟以下涧壑中。岩石色虽皓白。而颇杂青气。其质亦非真粹。自俞泓窟以上始变。而至是益纯洁。又自谷口以来。四十里间。绝无湍瀑喷薄之观。至是始见之。而尚逊于万瀑洞之奇壮。独峰壁映发之胜。可与之相抗而或过之耳。潭之南。有巨岩屹然。攀缘而登。俯仰眺临。所见益奇。水帘之上。白石平广。亘数十丈。又上数百步许。盘石平布百馀丈。溪水散布其上。流若绮縠。亦可玩也。闻更上十五里有大双瀑。共泻一潭。名十二瀑。特为奇异。而倦甚不能进。但见奇峰秀嶂。稠叠无穷而已。于是怅然而返。复至水帘上盘石午饭。倘佯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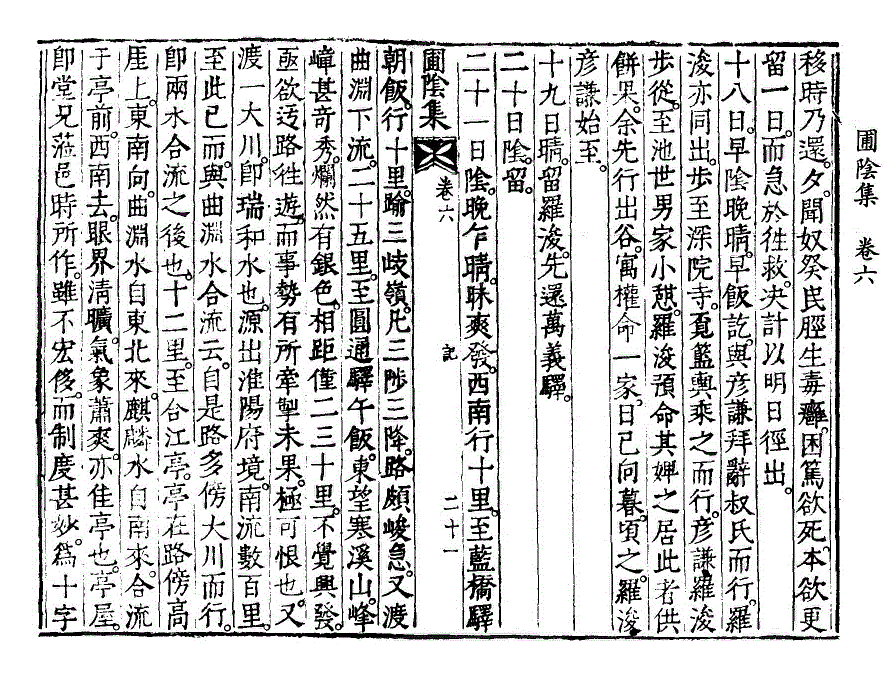 移时乃还。夕。闻奴癸民胫生毒痈。困笃欲死。本欲更留一日。而急于往救。决计以明日径出。
移时乃还。夕。闻奴癸民胫生毒痈。困笃欲死。本欲更留一日。而急于往救。决计以明日径出。十八日。早阴晚晴。早饭讫。与彦谦拜辞叔氏而行。罗浚亦同出。步至深院寺。觅篮舆乘之而行。彦谦,罗浚步从。至池世男家小憩。罗浚预命其婢之居此者供饼果。余先行出谷。寓权命一家。日已向暮。顷之。罗浚,彦谦始至。
十九日晴。留罗浚。先还万义驿。
二十日阴。留。
二十一日阴。晚乍晴。昧爽发。西南行十里。至蓝桥驿朝饭。行十里。踰三歧岭。凡三陟三降。路颇峻急。又渡曲渊下流。二十五里。至圆通驿午饭。东望寒溪山。峰嶂甚奇秀。烂然有银色。相距仅二三十里。不觉兴发。亟欲迂路往游。而事势有所牵掣未果。极可恨也。又渡一大川。即瑞和水也。源出淮阳府境。南流数百里。至此已而。与曲渊水合流云。自是路多傍大川而行。即两水合流之后也。十二里。至合江亭。亭在路傍高厓上。东南向。曲渊水自东北来。麒麟水自南来。合流于亭前。西南去。眼界清旷。气象萧爽。亦佳亭也。亭屋。即堂兄莅邑时所作。虽不宏侈。而制度甚妙。为十字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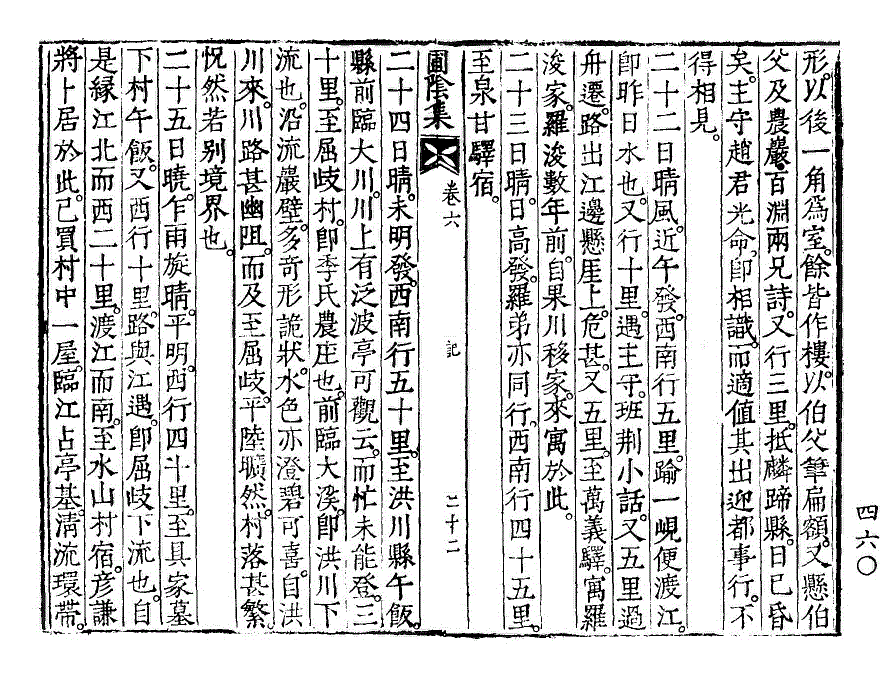 形。以后一角为室。馀皆作楼。以伯父笔扁额。又悬伯父及农岩,百渊两兄诗。又行三里。抵麟蹄县。日已昏矣。主守赵君光命。即相识。而适值其出迎都事行。不得相见。
形。以后一角为室。馀皆作楼。以伯父笔扁额。又悬伯父及农岩,百渊两兄诗。又行三里。抵麟蹄县。日已昏矣。主守赵君光命。即相识。而适值其出迎都事行。不得相见。二十二日晴风。近午发。西南行五里。踰一岘便渡江。即昨日水也。又行十里。遇主守。班荆小话。又五里过舟迁。路出江边悬厓上。危甚。又五里。至万义驿。寓罗浚家。罗浚数年前。自果川移家。来寓于此。
二十三日晴。日高发。罗弟亦同行。西南行四十五里。至泉甘驿宿。
二十四日晴。未明发。西南行五十里。至洪川县午饭。县前临大川。川上有泛波亭可观云。而忙未能登。三十里。至屈歧村。即季氏农庄也。前临大溪。即洪川下流也。沿流岩壁。多奇形诡状。水色亦澄碧可喜。自洪川来。川路甚幽阻。而及至屈歧。平陆旷然。村落甚繁。恍然若别境界也。
二十五日晓。乍雨旋晴。平明。西行四十里。至具家墓下村午饭。又西行十里。路与江遇。即屈歧下流也。自是缘江北而西二十里。渡江而南。至水山村宿。彦谦将卜居于此。已买村中一屋。临江占亭基。清流环带。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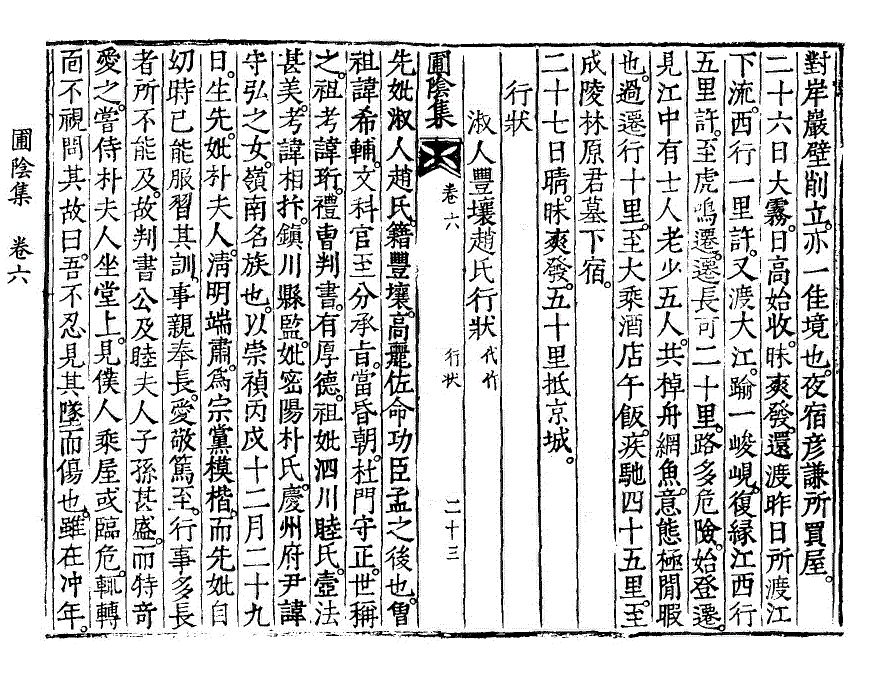 对岸岩壁削立。亦一佳境也。夜宿彦谦所买屋。
对岸岩壁削立。亦一佳境也。夜宿彦谦所买屋。二十六日大雾。日高始收。昧爽发。还渡昨日所渡江下流。西行一里许。又渡大江。踰一峻岘。复缘江西行五里许。至虎鸣迁。迁长可二十里。路多危险。始登迁。见江中有士人老少五人。共棹舟网鱼。意态极閒暇也。过迁行十里。至大乘酒店午饭。疾驰四十五里。至成陵林原君墓下宿。
二十七日晴。昧爽发。五十里抵京城。
圃阴集卷之六(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行状
淑人丰壤赵氏行状(代作)
先妣淑人赵氏。籍丰壤。高丽佐命功臣孟之后也。曾祖讳希辅。文科官至分承旨。当昏朝。杜门守正。世称之。祖考讳珩。礼曹判书。有厚德。祖妣泗川睦氏。壸法甚美。考讳相抃。镇川县监。妣密阳朴氏。庆州府尹讳守弘之女。岭南名族也。以崇祯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先。妣朴夫人。清明端肃。为宗党模楷。而先妣自幼时已能服习其训。事亲奉长。爱敬笃至。行事多长者所不能及。故判书公及睦夫人子孙甚盛。而特奇爱之。尝侍朴夫人坐堂上。见仆人乘屋或临危。辄转面不视问其故曰。吾不忍见其坠而伤也。虽在冲年。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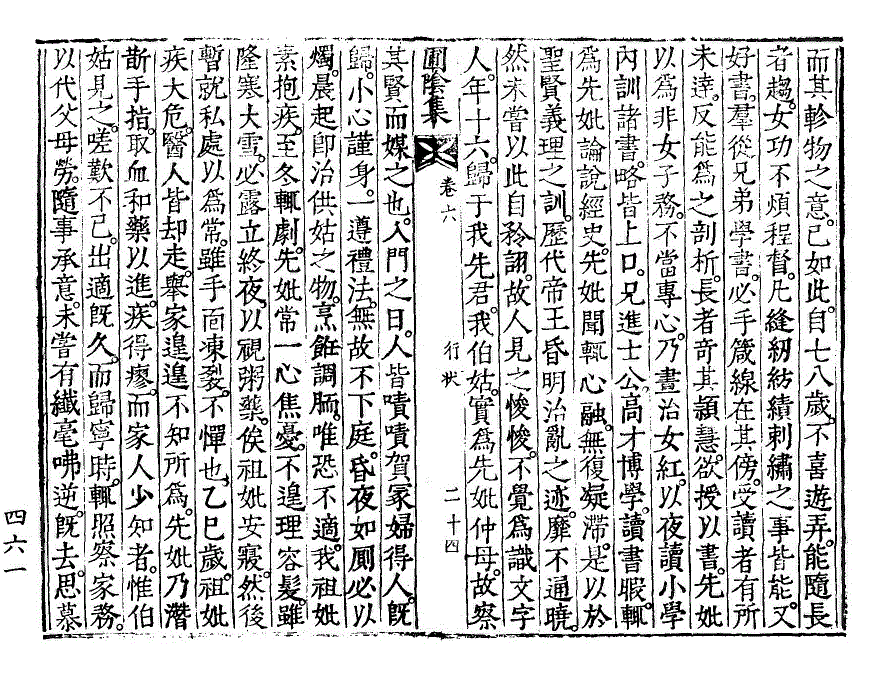 而其轸物之意。已如此。自七八岁。不喜游弄。能随长者趋。女功不烦程督。凡缝纫纺绩刺绣之事皆能。又好书。群从兄弟学书。必手箴线在其傍。受读者有所未达。反能为之剖析。长者奇其颖慧。欲授以书。先妣以为非女子务。不当专心。乃昼治女红。以夜读小学内训诸书。略皆上口。兄进士公。高才博学。读书暇。辄为先妣论说经史。先妣闻辄心融。无复凝滞。是以于圣贤义理之训。历代帝王昏明治乱之迹。靡不通晓。然未尝以此自矜诩。故人见之悛悛。不觉为识文字人。年十六。归于我先君。我伯姑。实为先妣仲母。故察其贤而媒之也。入门之日。人皆啧啧贺冢妇得人。既归。小心谨身。一遵礼法。无故不下庭。昏夜如厕必以烛。晨起即治供姑之物。烹饪调胹。唯恐不适。我祖妣素抱疾。至冬辄剧。先妣常一心焦忧。不遑理容发。虽隆寒大雪。必露立终夜。以视粥药。俟祖妣安寝。然后暂就私处以为常。虽手面冻裂。不惮也。乙巳岁。祖妣疾大危。医人皆却走。举家遑遑不知所为。先妣乃潜斮手指。取血和药以进。疾得瘳。而家人少知者。惟伯姑见之。嗟叹不已。出适既久。而归宁时。辄照察家务。以代父母劳。随事承意。未尝有纤毫咈逆。既去。思慕
而其轸物之意。已如此。自七八岁。不喜游弄。能随长者趋。女功不烦程督。凡缝纫纺绩刺绣之事皆能。又好书。群从兄弟学书。必手箴线在其傍。受读者有所未达。反能为之剖析。长者奇其颖慧。欲授以书。先妣以为非女子务。不当专心。乃昼治女红。以夜读小学内训诸书。略皆上口。兄进士公。高才博学。读书暇。辄为先妣论说经史。先妣闻辄心融。无复凝滞。是以于圣贤义理之训。历代帝王昏明治乱之迹。靡不通晓。然未尝以此自矜诩。故人见之悛悛。不觉为识文字人。年十六。归于我先君。我伯姑。实为先妣仲母。故察其贤而媒之也。入门之日。人皆啧啧贺冢妇得人。既归。小心谨身。一遵礼法。无故不下庭。昏夜如厕必以烛。晨起即治供姑之物。烹饪调胹。唯恐不适。我祖妣素抱疾。至冬辄剧。先妣常一心焦忧。不遑理容发。虽隆寒大雪。必露立终夜。以视粥药。俟祖妣安寝。然后暂就私处以为常。虽手面冻裂。不惮也。乙巳岁。祖妣疾大危。医人皆却走。举家遑遑不知所为。先妣乃潜斮手指。取血和药以进。疾得瘳。而家人少知者。惟伯姑见之。嗟叹不已。出适既久。而归宁时。辄照察家务。以代父母劳。随事承意。未尝有纤毫咈逆。既去。思慕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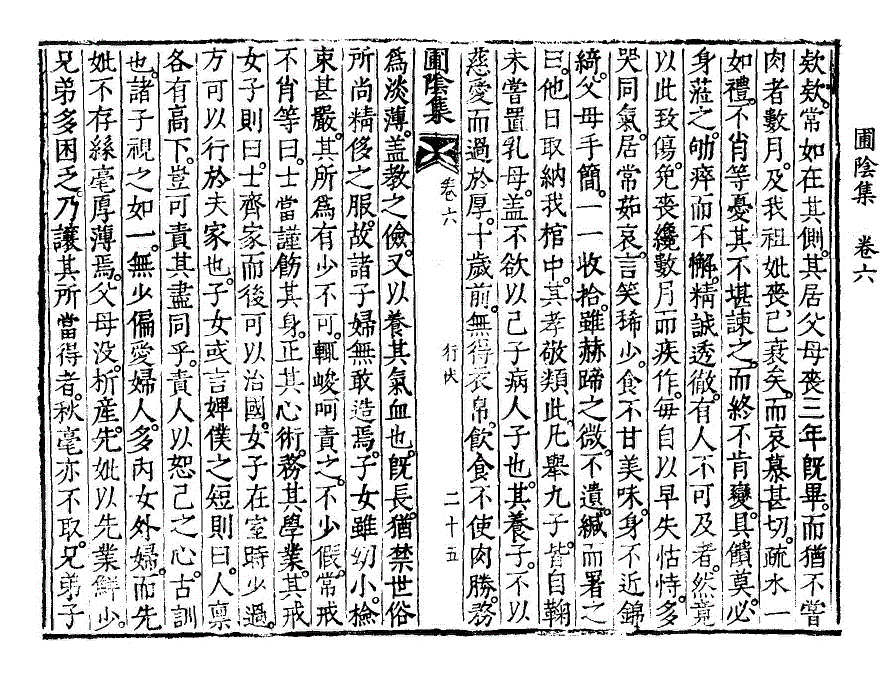 款款。常如在其侧。其居父母丧三年既毕。而犹不尝肉者数月。及我祖妣丧。已衰矣。而哀慕甚切。疏水一如礼。不肖等忧其不堪谏之。而终不肯变。具馈奠。必身莅之。劬瘁而不懈。精诚透彻。有人不可及者。然竟以此致伤。免丧才数月而疾作。每自以早失怙恃。多哭同气。居常茹哀。言笑稀少。食不甘美味。身不近锦绮。父母手简。一一收拾。虽赫蹄之微。不遗。缄而署之曰。他日取纳我棺中。其孝敬类此。凡举九子。皆自鞠未尝置乳母。盖不欲以己子病人子也。其养子。不以慈爱而过于厚。十岁前。无得衣帛。饮食不使肉胜。务为淡薄。盖教之俭。又以养其气血也。既长。犹禁世俗所尚精侈之服。故诸子妇无敢造焉。子女虽幼小。检束甚严。其所为有少不可。辄峻呵责之。不少假。常戒不肖等曰。士当谨饬其身。正其心术。务其学业。其戒女子则曰。士齐家而后可以治国。女子在室时少过。方可以行于夫家也。子女或言婢仆之短则曰。人禀各有高下。岂可责其尽同乎。责人以恕己之心。古训也。诸子视之如一。无少偏爱妇人。多内女外妇。而先妣不存丝毫厚薄焉。父母没。析产。先妣以先业鲜少。兄弟多困乏。乃让其所当得者。秋毫亦不取。兄弟子
款款。常如在其侧。其居父母丧三年既毕。而犹不尝肉者数月。及我祖妣丧。已衰矣。而哀慕甚切。疏水一如礼。不肖等忧其不堪谏之。而终不肯变。具馈奠。必身莅之。劬瘁而不懈。精诚透彻。有人不可及者。然竟以此致伤。免丧才数月而疾作。每自以早失怙恃。多哭同气。居常茹哀。言笑稀少。食不甘美味。身不近锦绮。父母手简。一一收拾。虽赫蹄之微。不遗。缄而署之曰。他日取纳我棺中。其孝敬类此。凡举九子。皆自鞠未尝置乳母。盖不欲以己子病人子也。其养子。不以慈爱而过于厚。十岁前。无得衣帛。饮食不使肉胜。务为淡薄。盖教之俭。又以养其气血也。既长。犹禁世俗所尚精侈之服。故诸子妇无敢造焉。子女虽幼小。检束甚严。其所为有少不可。辄峻呵责之。不少假。常戒不肖等曰。士当谨饬其身。正其心术。务其学业。其戒女子则曰。士齐家而后可以治国。女子在室时少过。方可以行于夫家也。子女或言婢仆之短则曰。人禀各有高下。岂可责其尽同乎。责人以恕己之心。古训也。诸子视之如一。无少偏爱妇人。多内女外妇。而先妣不存丝毫厚薄焉。父母没。析产。先妣以先业鲜少。兄弟多困乏。乃让其所当得者。秋毫亦不取。兄弟子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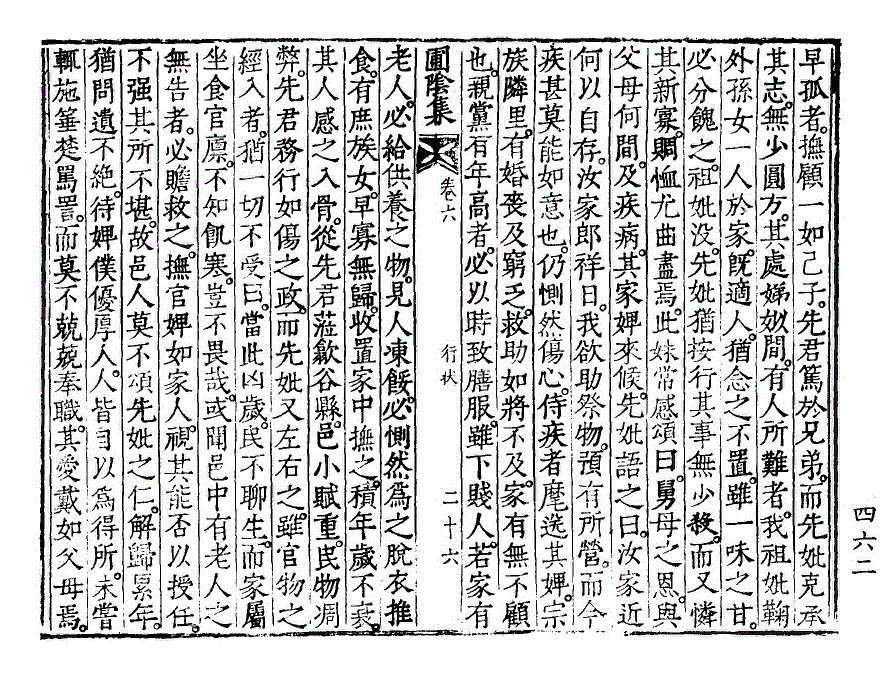 早孤者。抚顾一如己子。先君笃于兄弟。而先妣克承其志。无少圆方。其处娣姒间。有人所难者。我祖妣鞠外孙女一人于家。既适人。犹念之不置。虽一味之甘。必分馈之。祖妣没。先妣犹按行其事无少杀。而又怜其新寡。赒恤尤曲尽焉。此妹常感颂曰。舅母之恩。与父母何间。及疾病。其家婢来候。先妣语之曰。汝家近何以自存。汝家郎祥日。我欲助祭物。预有所营。而今疾甚莫能如意也。仍恻然伤心。侍疾者麾送其婢。宗族邻里。有婚丧及穷乏。救助如将不及。家有无不顾也。亲党有年高者。必以时致膳服。虽下贱人。若家有老人。必给供养之物。见人冻馁。必恻然为之脱衣推食。有庶族女。早寡无归。收置家中抚之。积年岁不衰。其人感之入骨。从先君莅歙谷县。邑小赋重。民物凋弊。先君务行如伤之政。而先妣又左右之。虽官物之经入者。犹一切不受曰。当此凶岁。民不聊生。而家属坐食官廪。不知饥寒。岂不畏哉。或闻邑中有老人之无告者。必赡救之。抚官婢如家人。视其能否以授任。不强其所不堪。故邑人莫不颂先妣之仁。解归累年。犹问遗不绝。待婢仆优厚人。人皆自以为得所。未尝辄施箠楚骂詈。而莫不兢兢奉职。其爱戴如父母焉。
早孤者。抚顾一如己子。先君笃于兄弟。而先妣克承其志。无少圆方。其处娣姒间。有人所难者。我祖妣鞠外孙女一人于家。既适人。犹念之不置。虽一味之甘。必分馈之。祖妣没。先妣犹按行其事无少杀。而又怜其新寡。赒恤尤曲尽焉。此妹常感颂曰。舅母之恩。与父母何间。及疾病。其家婢来候。先妣语之曰。汝家近何以自存。汝家郎祥日。我欲助祭物。预有所营。而今疾甚莫能如意也。仍恻然伤心。侍疾者麾送其婢。宗族邻里。有婚丧及穷乏。救助如将不及。家有无不顾也。亲党有年高者。必以时致膳服。虽下贱人。若家有老人。必给供养之物。见人冻馁。必恻然为之脱衣推食。有庶族女。早寡无归。收置家中抚之。积年岁不衰。其人感之入骨。从先君莅歙谷县。邑小赋重。民物凋弊。先君务行如伤之政。而先妣又左右之。虽官物之经入者。犹一切不受曰。当此凶岁。民不聊生。而家属坐食官廪。不知饥寒。岂不畏哉。或闻邑中有老人之无告者。必赡救之。抚官婢如家人。视其能否以授任。不强其所不堪。故邑人莫不颂先妣之仁。解归累年。犹问遗不绝。待婢仆优厚人。人皆自以为得所。未尝辄施箠楚骂詈。而莫不兢兢奉职。其爱戴如父母焉。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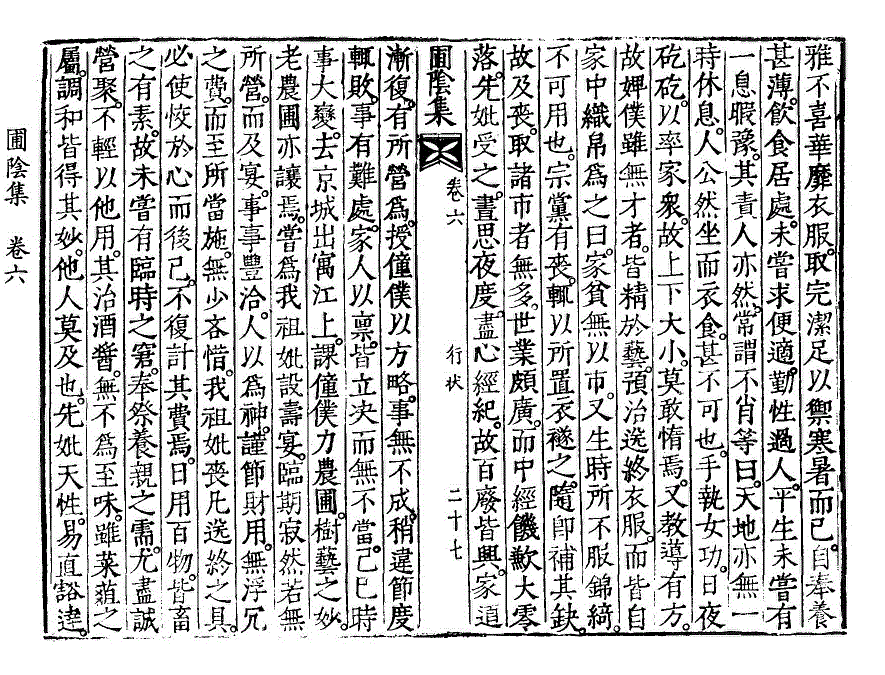 雅不喜华靡衣服。取完洁足以御寒暑而已。自奉养甚薄。饮食居处。未尝求便适。勤性过人。平生未尝有一息暇豫。其责人亦然。常谓不肖等曰。天地亦无一时休息。人公然坐而衣食。甚不可也。手执女功。日夜矻矻。以率家众。故上下大小。莫敢惰焉。又教导有方。故婢仆虽无才者。皆精于艺。预治送终衣服。而皆自家中织帛为之曰。家贫无以市。又生时所不服锦绮。不可用也。宗党有丧。辄以所置衣襚之。随即补其缺。故及丧。取诸市者无多。世业颇广。而中经饥歉大零落。先妣受之。昼思夜度。尽心经纪。故百废皆兴。家道渐复。有所营为。授僮仆以方略。事无不成。稍违节度辄败。事有难处。家人以禀。皆立决而无不当。己巳时事大变。去京城出寓江上。课僮仆力农圃。树艺之妙。老农圃亦让焉。尝为我祖妣设寿宴。临期寂然若无所营。而及宴。事事丰洽。人以为神。谨节财用。无浮冗之费。而至所当施。无少吝惜。我祖妣丧凡送终之具。必使恔于心而后已。不复计其费焉。日用百物。皆畜之有素。故未尝有临时之窘。奉祭养亲之需。尤尽诚营聚。不轻以他用。其治酒酱。无不为至味。虽菜菹之属。调和皆得其妙。他人莫及也。先妣天性。易直豁达。
雅不喜华靡衣服。取完洁足以御寒暑而已。自奉养甚薄。饮食居处。未尝求便适。勤性过人。平生未尝有一息暇豫。其责人亦然。常谓不肖等曰。天地亦无一时休息。人公然坐而衣食。甚不可也。手执女功。日夜矻矻。以率家众。故上下大小。莫敢惰焉。又教导有方。故婢仆虽无才者。皆精于艺。预治送终衣服。而皆自家中织帛为之曰。家贫无以市。又生时所不服锦绮。不可用也。宗党有丧。辄以所置衣襚之。随即补其缺。故及丧。取诸市者无多。世业颇广。而中经饥歉大零落。先妣受之。昼思夜度。尽心经纪。故百废皆兴。家道渐复。有所营为。授僮仆以方略。事无不成。稍违节度辄败。事有难处。家人以禀。皆立决而无不当。己巳时事大变。去京城出寓江上。课僮仆力农圃。树艺之妙。老农圃亦让焉。尝为我祖妣设寿宴。临期寂然若无所营。而及宴。事事丰洽。人以为神。谨节财用。无浮冗之费。而至所当施。无少吝惜。我祖妣丧凡送终之具。必使恔于心而后已。不复计其费焉。日用百物。皆畜之有素。故未尝有临时之窘。奉祭养亲之需。尤尽诚营聚。不轻以他用。其治酒酱。无不为至味。虽菜菹之属。调和皆得其妙。他人莫及也。先妣天性。易直豁达。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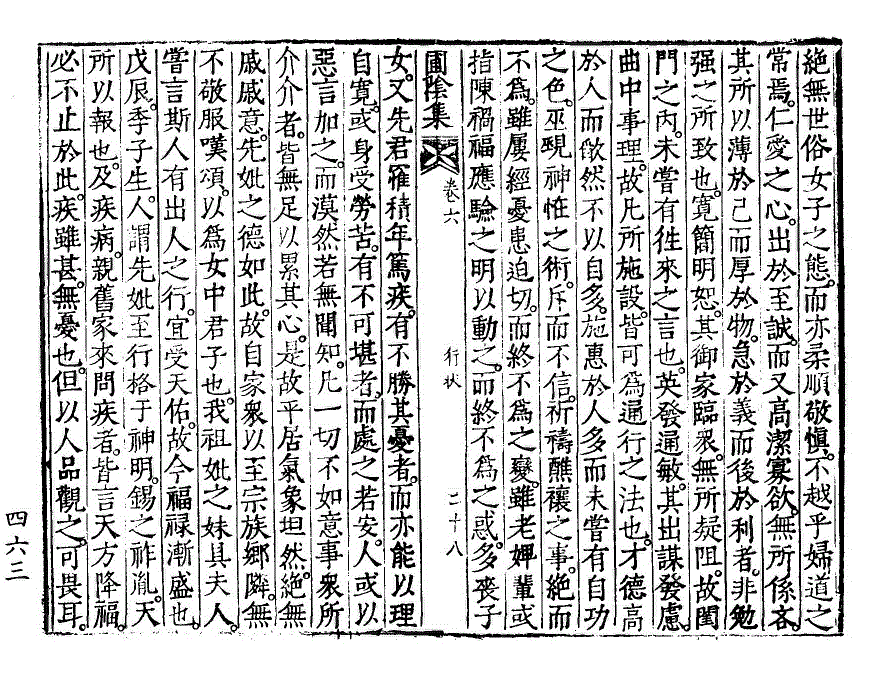 绝无世俗女子之态。而亦柔顺敬慎。不越乎妇道之常焉。仁爱之心。出于至诚。而又高洁寡欲。无所系吝。其所以薄于己而厚于物。急于义而后于利者。非勉强之所致也。宽简明恕。其御家临众。无所疑阻。故闺门之内。未尝有往来之言也。英发通敏。其出谋发虑。曲中事理。故凡所施设。皆可为通行之法也。才德高于人而欿然不以自多。施惠于人多而未尝有自功之色。巫觋神怪之术。斥而不信。祈祷醮禳之事。绝而不为。虽屡经忧患迫切。而终不为之变。虽老婢辈或指陈祸福应验之明以动之。而终不为之惑。多丧子女。又先君罹积年笃疾。有不胜其忧者。而亦能以理自宽。或身受劳苦。有不可堪者。而处之若安。人或以恶言加之。而漠然若无闻知。凡一切不如意事众所介介者。皆无足以累其心。是故平居气象坦然。绝无戚戚意。先妣之德如此。故自家众以至宗族乡邻。无不敬服叹颂。以为女中君子也。我祖妣之妹具夫人。尝言斯人有出人之行。宜受天佑。故今福禄渐盛也。戊辰。季子生。人谓先妣至行格于神明。锡之祚胤。天所以报也。及疾病。亲旧家来问疾者。皆言天方降福。必不止于此。疾虽甚。无忧也。但以人品观之。可畏耳。
绝无世俗女子之态。而亦柔顺敬慎。不越乎妇道之常焉。仁爱之心。出于至诚。而又高洁寡欲。无所系吝。其所以薄于己而厚于物。急于义而后于利者。非勉强之所致也。宽简明恕。其御家临众。无所疑阻。故闺门之内。未尝有往来之言也。英发通敏。其出谋发虑。曲中事理。故凡所施设。皆可为通行之法也。才德高于人而欿然不以自多。施惠于人多而未尝有自功之色。巫觋神怪之术。斥而不信。祈祷醮禳之事。绝而不为。虽屡经忧患迫切。而终不为之变。虽老婢辈或指陈祸福应验之明以动之。而终不为之惑。多丧子女。又先君罹积年笃疾。有不胜其忧者。而亦能以理自宽。或身受劳苦。有不可堪者。而处之若安。人或以恶言加之。而漠然若无闻知。凡一切不如意事众所介介者。皆无足以累其心。是故平居气象坦然。绝无戚戚意。先妣之德如此。故自家众以至宗族乡邻。无不敬服叹颂。以为女中君子也。我祖妣之妹具夫人。尝言斯人有出人之行。宜受天佑。故今福禄渐盛也。戊辰。季子生。人谓先妣至行格于神明。锡之祚胤。天所以报也。及疾病。亲旧家来问疾者。皆言天方降福。必不止于此。疾虽甚。无忧也。但以人品观之。可畏耳。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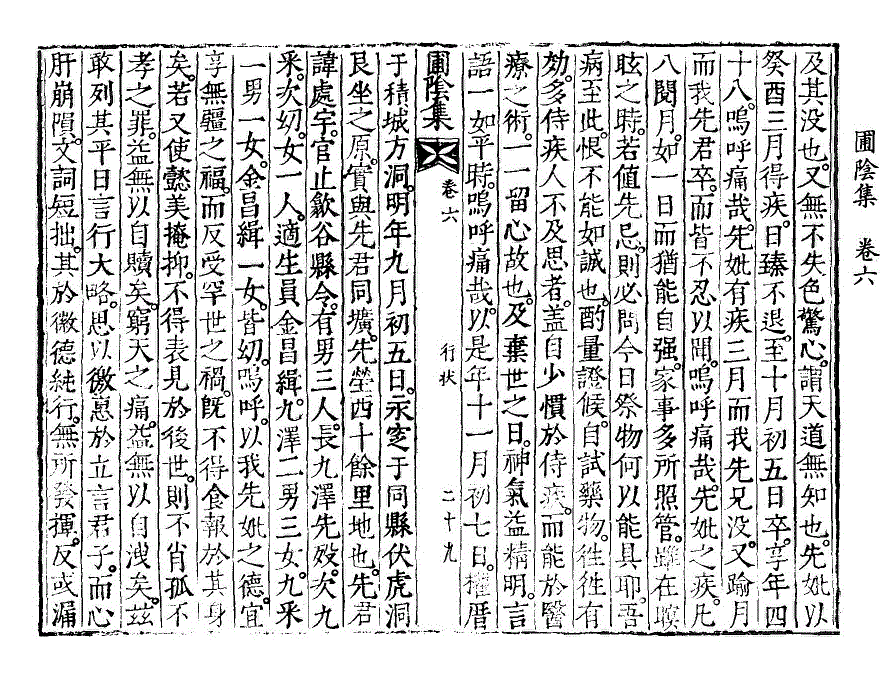 及其没也。又无不失色惊心。谓天道无知也。先妣以癸酉三月得疾。日臻不退。至十月初五日卒。享年四十八。呜呼痛哉。先妣有疾三月而我先兄没。又踰月而我先君卒。而皆不忍以闻。呜呼痛哉。先妣之疾。凡八阅月。如一日而犹能自强。家事多所照管。虽在瞑眩之时。若值先忌。则必问今日祭物何以能具耶。吾病至此。恨不能如诚也。酌量證候。自试药物。往往有效。多侍疾人不及思者。盖自少惯于侍疾。而能于医疗之术。一一留心故也。及弃世之日。神气益精明。言语一如平时。呜呼痛哉。以是年十一月初七日。权厝于积城方洞。明年九月初五日。永窆于同县伏虎洞艮坐之原。实与先君同圹。先茔西十馀里地也。先君讳处宇。官止歙谷县令。有男三人。长九泽先殁。次九采。次幼。女一人。适生员金昌缉。九泽二男三女。九采一男一女。金昌缉一女。皆幼。呜呼。以我先妣之德。宜享无疆之福。而反受罕世之祸。既不得食报于其身矣。若又使懿美掩抑。不得表见于后世。则不肖孤不孝之罪。益无以自赎矣。穷天之痛。益无以自泄矣。玆敢列其平日言行大略。思以徼惠于立言君子。而心肝崩陨。文词短拙。其于徽德纯行。无所发挥。反或漏
及其没也。又无不失色惊心。谓天道无知也。先妣以癸酉三月得疾。日臻不退。至十月初五日卒。享年四十八。呜呼痛哉。先妣有疾三月而我先兄没。又踰月而我先君卒。而皆不忍以闻。呜呼痛哉。先妣之疾。凡八阅月。如一日而犹能自强。家事多所照管。虽在瞑眩之时。若值先忌。则必问今日祭物何以能具耶。吾病至此。恨不能如诚也。酌量證候。自试药物。往往有效。多侍疾人不及思者。盖自少惯于侍疾。而能于医疗之术。一一留心故也。及弃世之日。神气益精明。言语一如平时。呜呼痛哉。以是年十一月初七日。权厝于积城方洞。明年九月初五日。永窆于同县伏虎洞艮坐之原。实与先君同圹。先茔西十馀里地也。先君讳处宇。官止歙谷县令。有男三人。长九泽先殁。次九采。次幼。女一人。适生员金昌缉。九泽二男三女。九采一男一女。金昌缉一女。皆幼。呜呼。以我先妣之德。宜享无疆之福。而反受罕世之祸。既不得食报于其身矣。若又使懿美掩抑。不得表见于后世。则不肖孤不孝之罪。益无以自赎矣。穷天之痛。益无以自泄矣。玆敢列其平日言行大略。思以徼惠于立言君子。而心肝崩陨。文词短拙。其于徽德纯行。无所发挥。反或漏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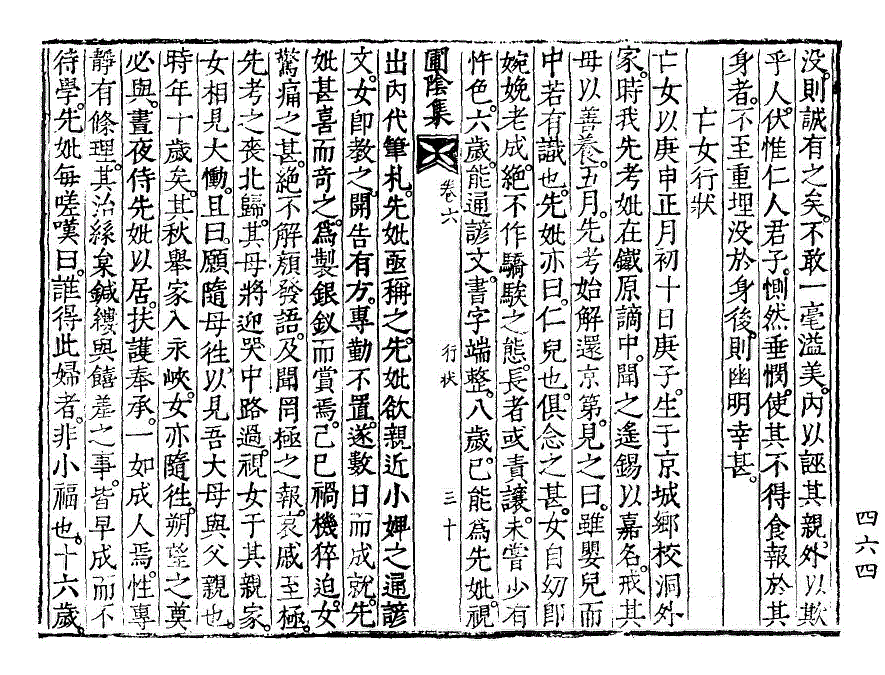 没。则诚有之矣。不敢一毫溢美。内以诬其亲。外以欺乎人。伏惟仁人君子。恻然垂悯。使其不得食报于其身者。不至重埋没于身后。则幽明幸甚。
没。则诚有之矣。不敢一毫溢美。内以诬其亲。外以欺乎人。伏惟仁人君子。恻然垂悯。使其不得食报于其身者。不至重埋没于身后。则幽明幸甚。亡女行状
亡女以庚申正月初十日庚子。生于京城乡校洞外家。时我先考妣在铁原谪中。闻之遥锡以嘉名。戒其母以善养。五月。先考始解还京第。见之曰。虽婴儿而中若有识也。先妣亦曰。仁儿也。俱念之甚。女自幼即婉娩老成。绝不作骄騃之态。长者或责让。未尝少有忤色。六岁。能通谚文。书字端整。八岁。已能为先妣。视出内代笔札。先妣亟称之。先妣欲亲近小婢之通谚文。女即教之。开告有方。专勤不置。遂数日而成就。先妣甚喜而奇之。为制银钗而赏焉。己巳祸机猝迫。女惊痛之甚。绝不解颜发语。及闻罔极之报。哀戚至极。先考之丧北归。其母将迎哭中路过。视女于其亲家。女相见大恸。且曰。愿随母往。以见吾大母与父亲也。时年十岁矣。其秋举家入永峡。女亦随往。朔望之奠必与。昼夜侍先妣以居。扶护奉承。一如成人焉。性专静有条理。其治丝枲针缕与饎羞之事。皆早成而不待学。先妣每嗟叹曰。谁得此妇者。非小福也。十六岁。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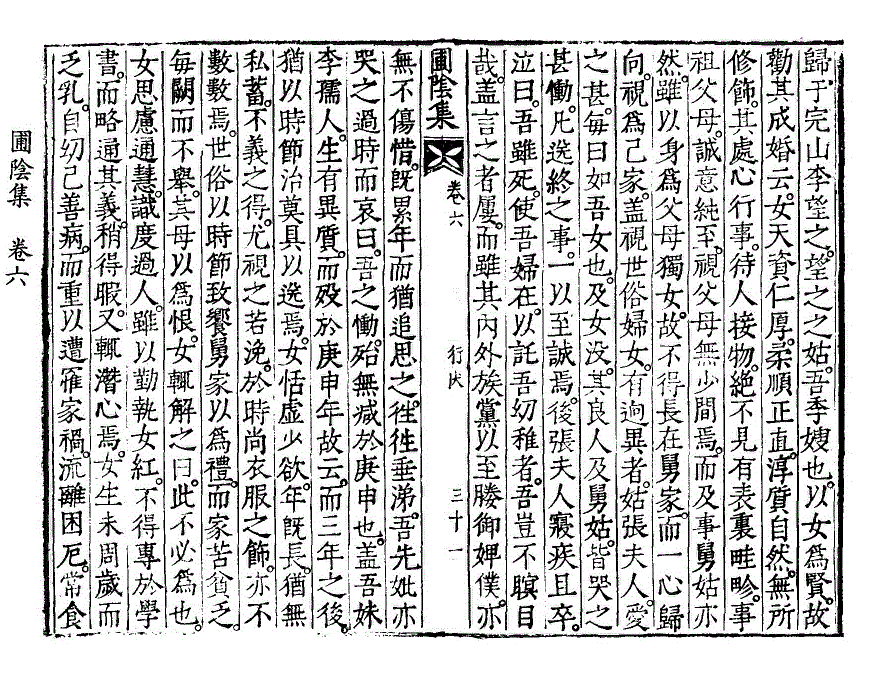 归于完山李望之。望之之姑。吾季嫂也。以女为贤。故劝其成婚云。女天资仁厚。柔顺正直。淳质自然。无所修饰。其处心行事。待人接物。绝不见有表里畦畛。事祖父母。诚意纯至。视父母无少间焉。而及事舅姑亦然。虽以身为父母独女。故不得长在舅家。而一心归向。视为己家。盖视世俗妇女。有迥异者。姑张夫人。爱之甚。每曰如吾女也。及女没。其良人及舅姑。皆哭之甚恸。凡送终之事。一以至诚焉。后张夫人寝疾且卒。泣曰。吾虽死。使吾妇在。以托吾幼稚者。吾岂不瞑目哉。盖言之者屡。而虽其内外族党以至媵御婢仆。亦无不伤惜。既累年而犹追思之。往往垂涕。吾先妣亦哭之过时而哀曰。吾之恸。殆无减于庚申也。盖吾妹李孺人。生有异质。而殁于庚申年故云。而三年之后。犹以时节治奠具以送焉。女恬虚少欲。年既长。犹无私蓄。不义之得。尤视之若浼。于时尚衣服之饰。亦不数数焉。世俗以时节致飨舅家以为礼。而家苦贫乏。每阙而不举。其母以为恨。女辄解之曰。此不必为也。女思虑通慧。识度过人。虽以勤执女红。不得专于学书。而略通其义。稍得暇。又辄潜心焉。女生未周岁而乏乳。自幼已善病。而重以遭罹家祸。流离困厄。常食
归于完山李望之。望之之姑。吾季嫂也。以女为贤。故劝其成婚云。女天资仁厚。柔顺正直。淳质自然。无所修饰。其处心行事。待人接物。绝不见有表里畦畛。事祖父母。诚意纯至。视父母无少间焉。而及事舅姑亦然。虽以身为父母独女。故不得长在舅家。而一心归向。视为己家。盖视世俗妇女。有迥异者。姑张夫人。爱之甚。每曰如吾女也。及女没。其良人及舅姑。皆哭之甚恸。凡送终之事。一以至诚焉。后张夫人寝疾且卒。泣曰。吾虽死。使吾妇在。以托吾幼稚者。吾岂不瞑目哉。盖言之者屡。而虽其内外族党以至媵御婢仆。亦无不伤惜。既累年而犹追思之。往往垂涕。吾先妣亦哭之过时而哀曰。吾之恸。殆无减于庚申也。盖吾妹李孺人。生有异质。而殁于庚申年故云。而三年之后。犹以时节治奠具以送焉。女恬虚少欲。年既长。犹无私蓄。不义之得。尤视之若浼。于时尚衣服之饰。亦不数数焉。世俗以时节致飨舅家以为礼。而家苦贫乏。每阙而不举。其母以为恨。女辄解之曰。此不必为也。女思虑通慧。识度过人。虽以勤执女红。不得专于学书。而略通其义。稍得暇。又辄潜心焉。女生未周岁而乏乳。自幼已善病。而重以遭罹家祸。流离困厄。常食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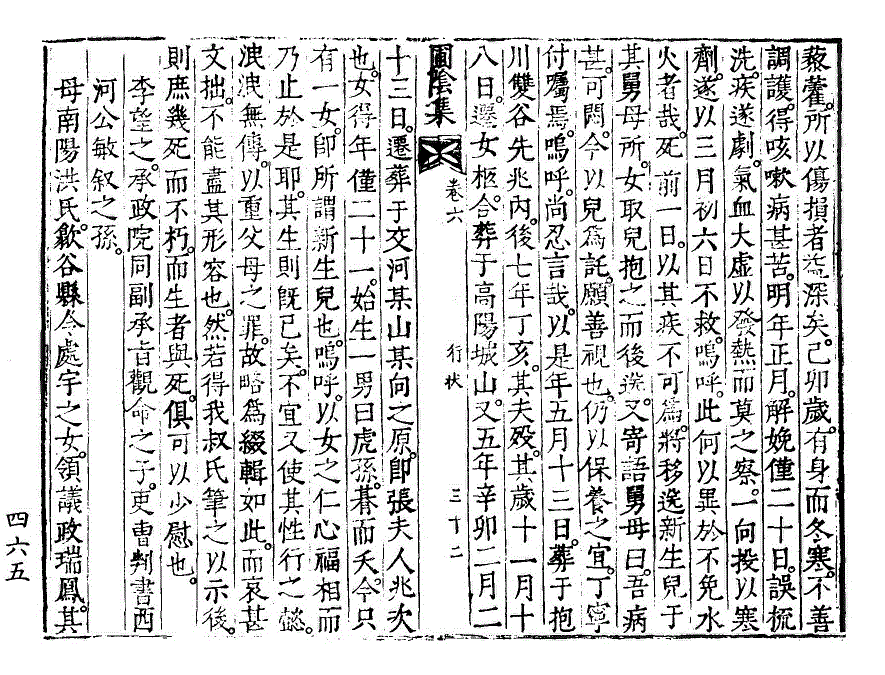 藜藿。所以伤损者益深矣。己卯岁。有身而冬寒。不善调护。得咳嗽病甚苦。明年正月。解娩仅二十日。误梳洗。疾遂剧。气血大虚以发热而莫之察。一向投以寒剂。遂以三月初六日不救。呜呼。此何以异于不免水火者哉。死前一日。以其疾不可为。将移送新生儿于其舅母所。女取儿抱之而后送。又寄语舅母曰。吾病甚。可闷。今以儿为托。愿善视也。仍以保养之宜。丁宁付嘱焉。呜呼。尚忍言哉。以是年五月十三日。葬于抱川双谷先兆内。后七年丁亥。其夫殁。其岁十一月十八日。迁女柩。合葬于高阳城山。又五年辛卯二月二十三日。迁葬于交河某山某向之原。即张夫人兆次也。女得年仅二十一。始生一男曰虎孙。期而夭。今只有一女。即所谓新生儿也。呜呼。以女之仁心福相而乃止于是耶。其生则既已矣。不宜又使其性行之懿。泯泯无传。以重父母之罪。故略为缀辑如此。而哀甚文拙。不能尽其形容也。然若得我叔氏笔之以示后。则庶几死而不朽。而生者与死。俱可以少慰也。
藜藿。所以伤损者益深矣。己卯岁。有身而冬寒。不善调护。得咳嗽病甚苦。明年正月。解娩仅二十日。误梳洗。疾遂剧。气血大虚以发热而莫之察。一向投以寒剂。遂以三月初六日不救。呜呼。此何以异于不免水火者哉。死前一日。以其疾不可为。将移送新生儿于其舅母所。女取儿抱之而后送。又寄语舅母曰。吾病甚。可闷。今以儿为托。愿善视也。仍以保养之宜。丁宁付嘱焉。呜呼。尚忍言哉。以是年五月十三日。葬于抱川双谷先兆内。后七年丁亥。其夫殁。其岁十一月十八日。迁女柩。合葬于高阳城山。又五年辛卯二月二十三日。迁葬于交河某山某向之原。即张夫人兆次也。女得年仅二十一。始生一男曰虎孙。期而夭。今只有一女。即所谓新生儿也。呜呼。以女之仁心福相而乃止于是耶。其生则既已矣。不宜又使其性行之懿。泯泯无传。以重父母之罪。故略为缀辑如此。而哀甚文拙。不能尽其形容也。然若得我叔氏笔之以示后。则庶几死而不朽。而生者与死。俱可以少慰也。李望之。承政院同副承旨观命之子。吏曹判书西河公敏叙之孙。
母南阳洪氏。歙谷县令处宇之女。领议政瑞凤。其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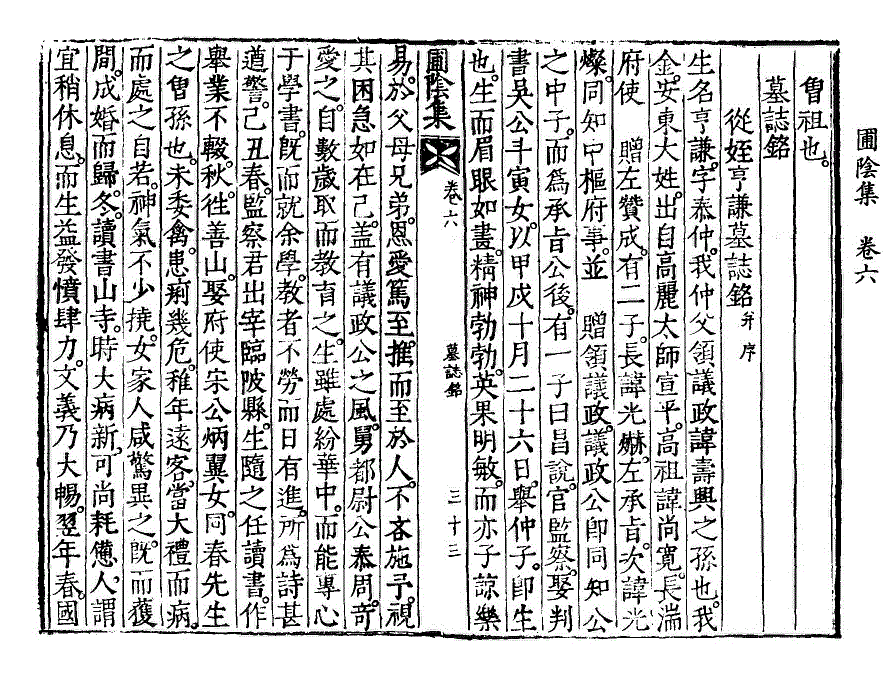 曾祖也。
曾祖也。圃阴集卷之六(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墓志铭
从侄亨谦墓志铭(并序)
生名亨谦。字泰仲。我仲父领议政讳寿兴之孙也。我金。安东大姓。出自高丽太师宣平。高祖讳尚宽。长湍府使 赠左赞成。有二子。长讳光赫。左承旨。次讳光灿。同知中枢府事。并 赠领议政。议政公即同知公之中子。而为承旨公后。有一子曰昌说。官监察。娶判书吴公斗寅女。以甲戌十月二十六日。举仲子。即生也。生而眉眼如画。精神勃勃。英果明敏。而亦子谅乐易。于父母兄弟。恩爱笃至。推而至于人。不吝施予。视其困急如在己。盖有议政公之风。舅都尉公泰周。奇爱之。自数岁取而教育之。生虽处纷华中。而能专心于学书。既而就余学。教者不劳而日有进。所为诗甚遒警。己丑春。监察君出宰临陂县。生随之任读书。作举业不辍。秋。往善山。娶府使宋公炳翼女。同春先生之曾孙也。未委禽。患痢几危。稚年远客。当大礼而病。而处之自若。神气不少挠。女家人咸惊异之。既而获间。成婚而归。冬。读书山寺。时大病新。可尚耗惫。人谓宜稍休息。而生益发愤肆力。文义乃大畅。翌年春。国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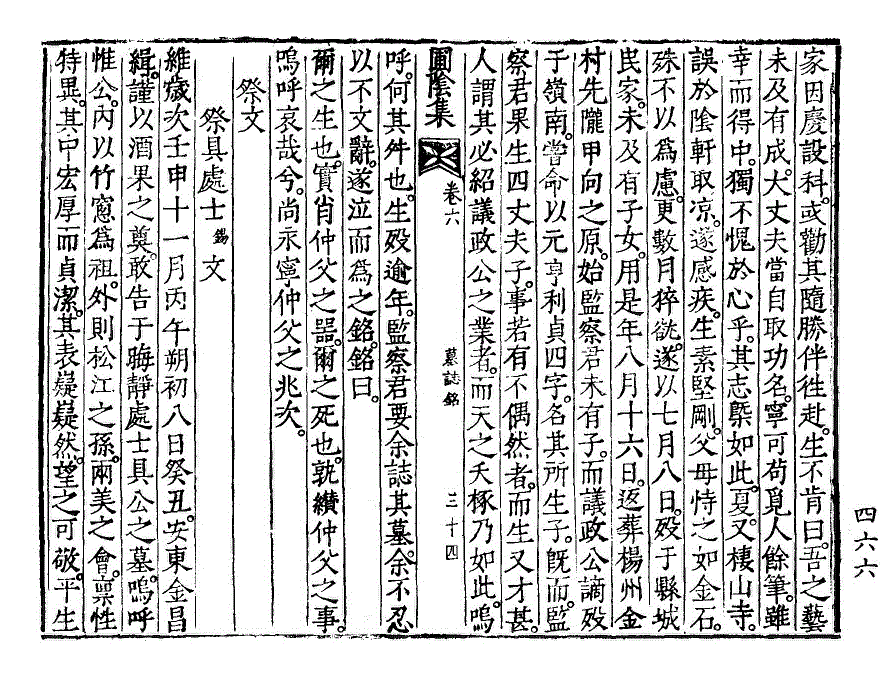 家因庆设科。或劝其随胜伴往赴。生不肯曰。吾之艺未及有成。大丈夫当自取功名。宁可苟觅人馀笔。虽幸而得中。独不愧于心乎。其志槩如此。夏。又栖山寺。误于阴轩取凉。遂感疾。生素坚刚。父母恃之如金石。殊不以为虑。更数月猝㞃。遂以七月八日。殁于县城民家。未及有子女。用是年八月十六日。返葬杨州金村先陇甲向之原。始监察君未有子。而议政公谪殁于岭南。尝命以元亨利贞四字。名其所生子。既而。监察君果生四丈夫子。事若有不偶然者。而生又才甚。人谓其必绍议政公之业者。而天之夭椓乃如此。呜呼。何其舛也。生殁逾年。监察君要余志其墓。余不忍以不文辞。遂泣而为之铭。铭曰。
家因庆设科。或劝其随胜伴往赴。生不肯曰。吾之艺未及有成。大丈夫当自取功名。宁可苟觅人馀笔。虽幸而得中。独不愧于心乎。其志槩如此。夏。又栖山寺。误于阴轩取凉。遂感疾。生素坚刚。父母恃之如金石。殊不以为虑。更数月猝㞃。遂以七月八日。殁于县城民家。未及有子女。用是年八月十六日。返葬杨州金村先陇甲向之原。始监察君未有子。而议政公谪殁于岭南。尝命以元亨利贞四字。名其所生子。既而。监察君果生四丈夫子。事若有不偶然者。而生又才甚。人谓其必绍议政公之业者。而天之夭椓乃如此。呜呼。何其舛也。生殁逾年。监察君要余志其墓。余不忍以不文辞。遂泣而为之铭。铭曰。尔之生也。实肖仲父之器。尔之死也。孰缵仲父之事。呜呼哀哉兮。尚永宁仲父之兆次。
圃阴集卷之六(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祭文
祭具处士(锡)文
维岁次壬申十一月丙午朔初八日癸丑。安东金昌缉。谨以酒果之奠。敢告于晦静处士具公之墓。呜呼惟公。内以竹窗为祖。外则松江之孙。两美之会。禀性特异。其中宏厚而贞洁。其表嶷嶷然。望之可敬。平生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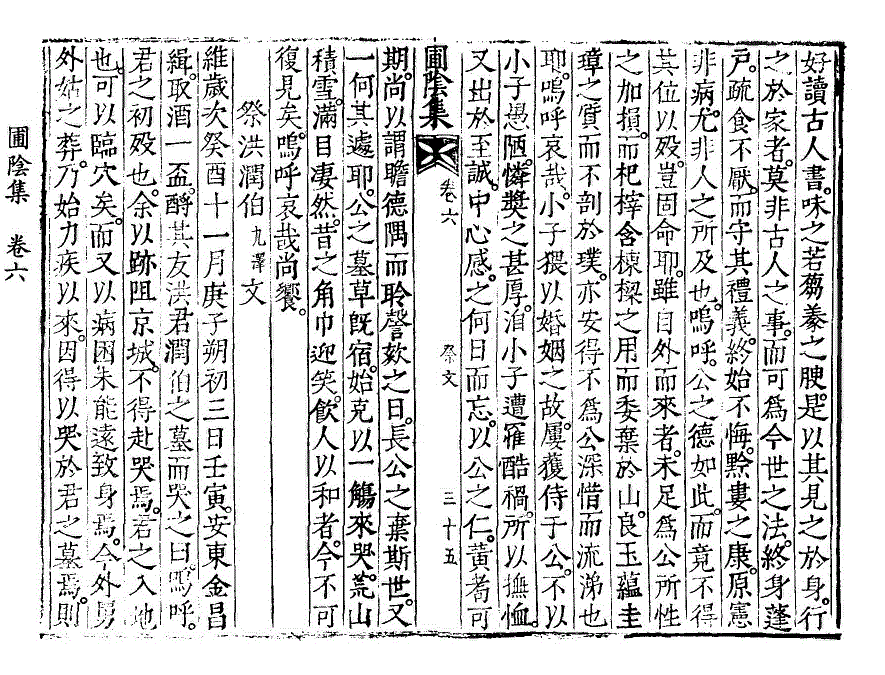 好读古人书。味之若刍豢之腴。是以其见之于身。行之于家者。莫非古人之事。而可为今世之法。终身蓬户。疏食不厌。而守其礼义。终始不悔。黔娄之康。原宪非病。尤非人之所及也。呜呼。公之德如此。而竟不得其位以殁。岂固命耶。虽自外而来者。未足为公所性之加损。而杞梓含栋梁之用而委弃于山。良玉蕴圭璋之质而不剖于璞。亦安得不为公深惜而流涕也耶。呜呼哀哉。小子猥以婚姻之故。屡获侍于公。不以小子愚陋。怜奖之甚厚。洎小子遭罹酷祸。所以抚恤。又出于至诚。中心感。之何日而忘。以公之仁。黄耇可期。尚以谓瞻德隅而聆謦欬之日。长公之弃斯世。又一何其遽耶。公之墓草既宿。始克以一觞来哭。荒山积雪。满目凄然。昔之角巾迎笑。饮人以和者。今不可复见矣。呜呼哀哉尚飨。
好读古人书。味之若刍豢之腴。是以其见之于身。行之于家者。莫非古人之事。而可为今世之法。终身蓬户。疏食不厌。而守其礼义。终始不悔。黔娄之康。原宪非病。尤非人之所及也。呜呼。公之德如此。而竟不得其位以殁。岂固命耶。虽自外而来者。未足为公所性之加损。而杞梓含栋梁之用而委弃于山。良玉蕴圭璋之质而不剖于璞。亦安得不为公深惜而流涕也耶。呜呼哀哉。小子猥以婚姻之故。屡获侍于公。不以小子愚陋。怜奖之甚厚。洎小子遭罹酷祸。所以抚恤。又出于至诚。中心感。之何日而忘。以公之仁。黄耇可期。尚以谓瞻德隅而聆謦欬之日。长公之弃斯世。又一何其遽耶。公之墓草既宿。始克以一觞来哭。荒山积雪。满目凄然。昔之角巾迎笑。饮人以和者。今不可复见矣。呜呼哀哉尚飨。祭洪润伯(九泽)文
维岁次癸酉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安东金昌缉。取酒一杯。酹其友洪君润伯之墓而哭之曰。呜呼。君之初殁也。余以迹阻京城。不得赴哭焉。君之入地也。可以临穴矣。而又以病困未能远致身焉。今外舅外姑之葬。乃始力疾以来。因得以哭于君之墓焉。则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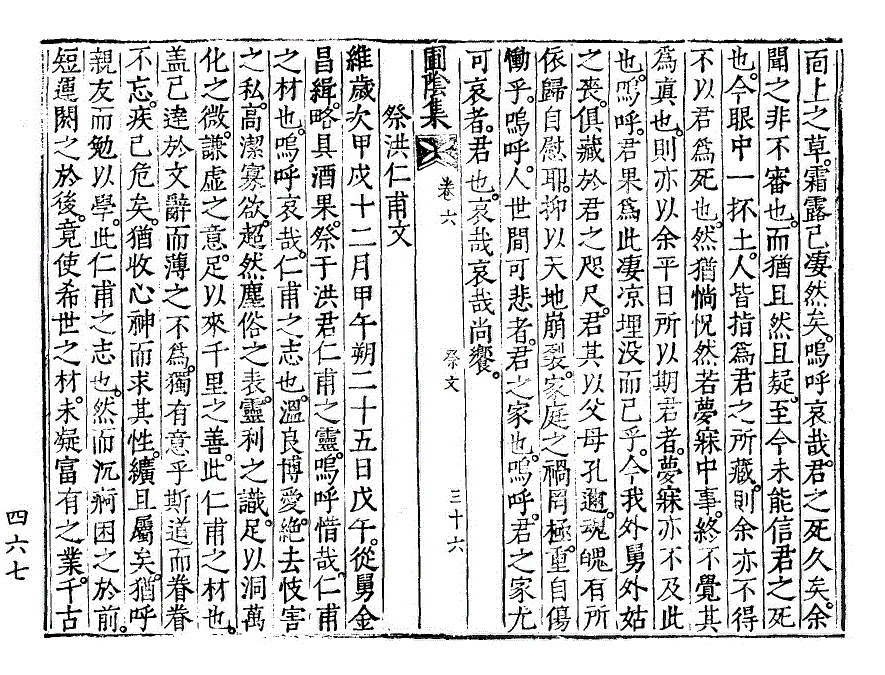 面上之草。霜露已凄然矣。呜呼哀哉。君之死久矣。余闻之非不审也。而犹且然且疑。至今未能信君之死也。今眼中一抔土。人皆指为君之所藏。则余亦不得不以君为死也。然犹惝恍然若梦寐中事。终不觉其为真也。则亦以余平日所以期君者。梦寐亦不及此也。呜呼。君果为此凄凉埋没而已乎。今我外舅外姑之丧。俱藏于君之咫尺。君其以父母孔迩。魂魄有所依归自慰耶。抑以天地崩裂。家庭之祸罔极。重自伤恸乎。呜呼。人世间可悲者。君之家也。呜呼。君之家尤可哀者。君也。哀哉哀哉尚飨。
面上之草。霜露已凄然矣。呜呼哀哉。君之死久矣。余闻之非不审也。而犹且然且疑。至今未能信君之死也。今眼中一抔土。人皆指为君之所藏。则余亦不得不以君为死也。然犹惝恍然若梦寐中事。终不觉其为真也。则亦以余平日所以期君者。梦寐亦不及此也。呜呼。君果为此凄凉埋没而已乎。今我外舅外姑之丧。俱藏于君之咫尺。君其以父母孔迩。魂魄有所依归自慰耶。抑以天地崩裂。家庭之祸罔极。重自伤恸乎。呜呼。人世间可悲者。君之家也。呜呼。君之家尤可哀者。君也。哀哉哀哉尚飨。祭洪仁甫文
维岁次甲戌十二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从舅金昌缉。略具酒果。祭于洪君仁甫之灵。呜呼惜哉。仁甫之材也。呜呼哀哉。仁甫之志也。温良博爱。绝去忮害之私。高洁寡欲。超然尘俗之表。灵利之识。足以洞万化之微。谦虚之意。足以来千里之善。此仁甫之材也。盖已达于文辞而薄之不为。独有意乎斯道而眷眷不忘。疾已危矣。犹收心神而求其性。纩且属矣。犹呼亲友而勉以学。此仁甫之志也。然而沉痾困之于前。短运阏之于后。竟使希世之材。未凝富有之业。千古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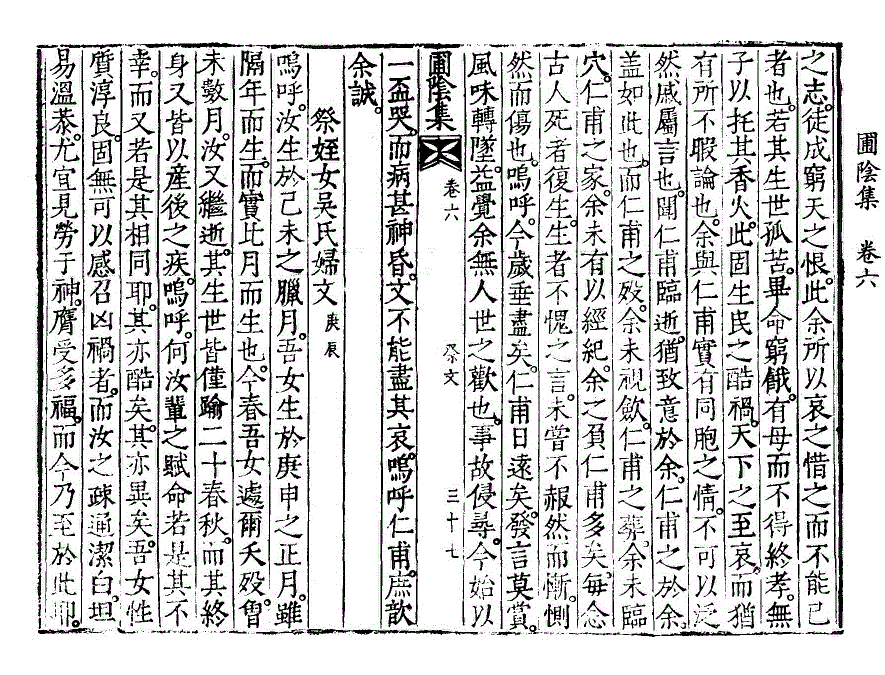 之志。徒成穷天之恨。此余所以哀之惜之而不能已者也。若其生世孤苦。毕命穷饿。有母而不得终孝。无子以托其香火。此固生民之酷祸。天下之至哀。而犹有所不暇论也。余与仁甫实有同胞之情。不可以泛然戚属言也。闻仁甫临逝。犹致意于余。仁甫之于余。盖如此也。而仁甫之殁。余未视敛。仁甫之葬。余未临穴。仁甫之家。余未有以经纪。余之负仁甫多矣。每念古人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之言。未尝不赧然而惭。恻然而伤也。呜呼。今岁垂尽矣。仁甫日远矣。发言莫赏。风味转坠。益觉余无人世之欢也。事故侵寻。今始以一杯哭。而病甚神昏。文不能尽其哀。呜呼仁甫。庶歆余诚。
之志。徒成穷天之恨。此余所以哀之惜之而不能已者也。若其生世孤苦。毕命穷饿。有母而不得终孝。无子以托其香火。此固生民之酷祸。天下之至哀。而犹有所不暇论也。余与仁甫实有同胞之情。不可以泛然戚属言也。闻仁甫临逝。犹致意于余。仁甫之于余。盖如此也。而仁甫之殁。余未视敛。仁甫之葬。余未临穴。仁甫之家。余未有以经纪。余之负仁甫多矣。每念古人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之言。未尝不赧然而惭。恻然而伤也。呜呼。今岁垂尽矣。仁甫日远矣。发言莫赏。风味转坠。益觉余无人世之欢也。事故侵寻。今始以一杯哭。而病甚神昏。文不能尽其哀。呜呼仁甫。庶歆余诚。祭侄女吴氏妇文(庚辰)
呜呼。汝生于己未之腊月。吾女生于庚申之正月。虽隔年而生。而实比月而生也。今春吾女遽尔夭殁。曾未数月。汝又继逝。其生世皆仅踰二十春秋。而其终身又皆以产后之疾。呜呼。何汝辈之赋命若是其不幸。而又若是其相同耶。其亦酷矣。其亦异矣。吾女性质淳良。固无可以感召凶祸者。而汝之疏通洁白。坦易温恭。尤宜见劳于神。膺受多福。而今乃至于此耶。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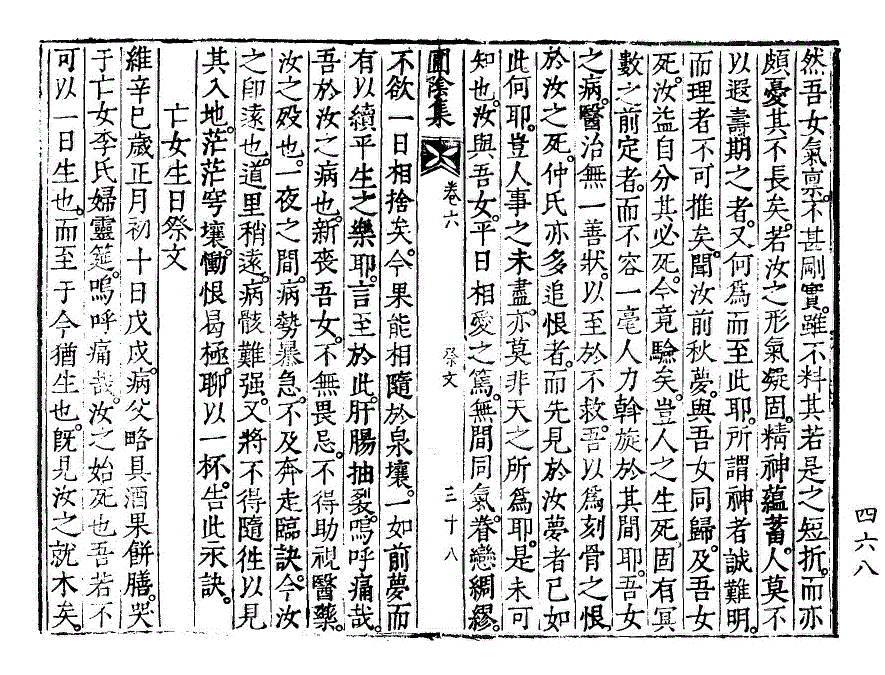 然吾女气禀。不甚刚实。虽不料其若是之短折。而亦颇忧其不长矣。若汝之形气凝固。精神蕴蓄。人莫不以遐寿期之者。又何为而至此耶。所谓神者诚难明。而理者不可推矣。闻汝前秋梦。与吾女同归。及吾女死。汝益自分其必死。今竟验矣。岂人之生死。固有冥数之前定者。而不容一毫人力斡旋于其间耶。吾女之病。医治无一善状。以至于不救。吾以为刻骨之恨。于汝之死。仲氏亦多追恨者。而先见于汝梦者已如此何耶。岂人事之未尽。亦莫非天之所为耶。是未可知也。汝与吾女。平日相爱之笃。无间同气。眷恋绸缪。不欲一日相舍矣。今果能相随于泉壤。一如前梦而有以续平生之乐耶。言至于此。肝肠抽裂。呜呼痛哉。吾于汝之病也。新丧吾女。不无畏忌。不得助视医药。汝之殁也。一夜之间。病势暴急。不及奔走临诀。今汝之即远也。道里稍远。病骸难强。又将不得随往以见其入地。茫茫穹壤。恸恨曷极。聊以一杯。告此永诀。
然吾女气禀。不甚刚实。虽不料其若是之短折。而亦颇忧其不长矣。若汝之形气凝固。精神蕴蓄。人莫不以遐寿期之者。又何为而至此耶。所谓神者诚难明。而理者不可推矣。闻汝前秋梦。与吾女同归。及吾女死。汝益自分其必死。今竟验矣。岂人之生死。固有冥数之前定者。而不容一毫人力斡旋于其间耶。吾女之病。医治无一善状。以至于不救。吾以为刻骨之恨。于汝之死。仲氏亦多追恨者。而先见于汝梦者已如此何耶。岂人事之未尽。亦莫非天之所为耶。是未可知也。汝与吾女。平日相爱之笃。无间同气。眷恋绸缪。不欲一日相舍矣。今果能相随于泉壤。一如前梦而有以续平生之乐耶。言至于此。肝肠抽裂。呜呼痛哉。吾于汝之病也。新丧吾女。不无畏忌。不得助视医药。汝之殁也。一夜之间。病势暴急。不及奔走临诀。今汝之即远也。道里稍远。病骸难强。又将不得随往以见其入地。茫茫穹壤。恸恨曷极。聊以一杯。告此永诀。亡女生日祭文
维辛巳岁正月初十日戊戌。病父略具酒果饼膳。哭于亡女李氏妇灵筵。呜呼痛哉。汝之始死也吾若不可以一日生也。而至于今犹生也。既见汝之就木矣。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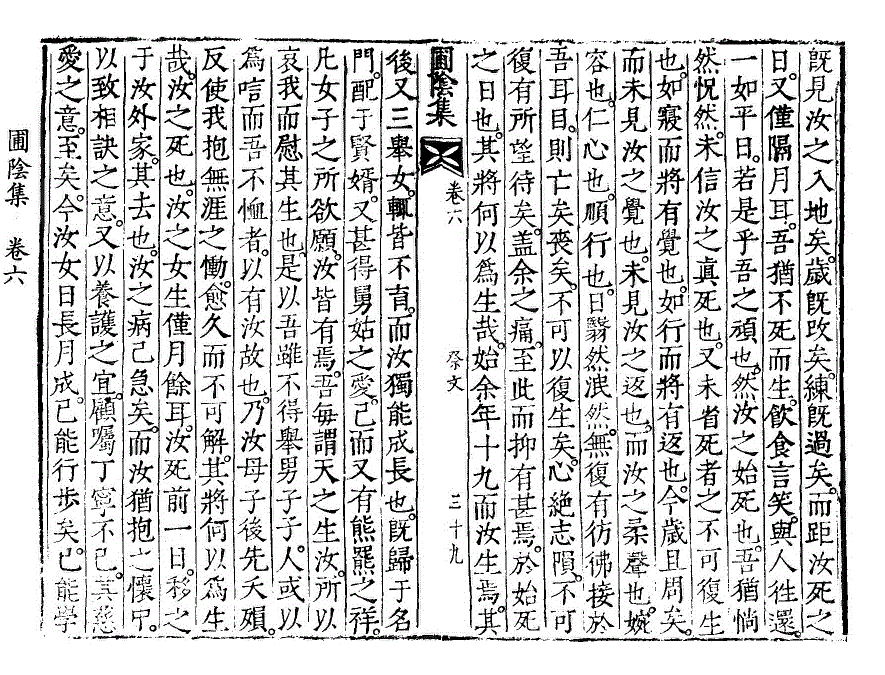 既见汝之入地矣。岁既改矣。练既过矣。而距汝死之日。又仅隔月耳。吾犹不死而生。饮食言笑。与人往还。一如平日。若是乎吾之顽也。然汝之始死也。吾犹惝然恍然。未信汝之真死也。又未省死者之不可复生也。如寝而将有觉也。如行而将有返也。今岁且周矣。而未见汝之觉也。未见汝之返也。而汝之柔声也。婉容也。仁心也。顺行也。日翳然泯然。无复有彷佛接于吾耳目。则亡矣丧矣。不可以复生矣。心绝志陨。不可复有所望待矣。盖余之痛。至此而抑有甚焉。于始死之日也。其将何以为生哉。始余年十九而汝生焉。其后又三举女。辄皆不育。而汝独能成长也。既归于名门。配于贤婿。又甚得舅姑之爱。已而又有熊罴之祥。凡女子之所欲愿。汝皆有焉。吾每谓天之生汝。所以哀我而慰其生也。是以吾虽不得举男子子。人或以为唁而吾不恤者。以有汝故也。乃汝母子后先夭殒。反使我抱无涯之恸。愈久而不可解。其将何以为生哉。汝之死也。汝之女生仅月馀耳。汝死前一日。移之于汝外家。其去也。汝之病已急矣。而汝犹抱之怀中。以致相诀之意。又以养护之宜。顾嘱丁宁不已。其慈爱之意。至矣。今汝女日长月成。已能行步矣。已能学
既见汝之入地矣。岁既改矣。练既过矣。而距汝死之日。又仅隔月耳。吾犹不死而生。饮食言笑。与人往还。一如平日。若是乎吾之顽也。然汝之始死也。吾犹惝然恍然。未信汝之真死也。又未省死者之不可复生也。如寝而将有觉也。如行而将有返也。今岁且周矣。而未见汝之觉也。未见汝之返也。而汝之柔声也。婉容也。仁心也。顺行也。日翳然泯然。无复有彷佛接于吾耳目。则亡矣丧矣。不可以复生矣。心绝志陨。不可复有所望待矣。盖余之痛。至此而抑有甚焉。于始死之日也。其将何以为生哉。始余年十九而汝生焉。其后又三举女。辄皆不育。而汝独能成长也。既归于名门。配于贤婿。又甚得舅姑之爱。已而又有熊罴之祥。凡女子之所欲愿。汝皆有焉。吾每谓天之生汝。所以哀我而慰其生也。是以吾虽不得举男子子。人或以为唁而吾不恤者。以有汝故也。乃汝母子后先夭殒。反使我抱无涯之恸。愈久而不可解。其将何以为生哉。汝之死也。汝之女生仅月馀耳。汝死前一日。移之于汝外家。其去也。汝之病已急矣。而汝犹抱之怀中。以致相诀之意。又以养护之宜。顾嘱丁宁不已。其慈爱之意。至矣。今汝女日长月成。已能行步矣。已能学圃阴集卷之六 第 469L 页
 语矣。其警慧之性。婉好之容。往往使余破涕为笑。而汝乃不及见之矣。是尚可忍耶。是尚可忍耶。方春草木萌动。蛰虫振作。万品欣欣举皆有昭苏之意。而汝独不能然。吾之痛当如何。而况今日又汝降生之辰也。每年此日。必有以饷汝。虽家贫不能盛为酒食。而所以祝汝寿福者。岂有穷哉。而今乃以此物。酹汝祭汝。此何为耶。此何为耶。汝柩之引也。余病惫特甚。又神魂错乱。为文告汝而不尽所欲言。其后每欲更抒腷臆。而辄哀塞不能成语而止矣。今因此奠酹。略告余哀。而终亦不能尽其意也。然汝其听而飨之乎。呜呼痛哉。
语矣。其警慧之性。婉好之容。往往使余破涕为笑。而汝乃不及见之矣。是尚可忍耶。是尚可忍耶。方春草木萌动。蛰虫振作。万品欣欣举皆有昭苏之意。而汝独不能然。吾之痛当如何。而况今日又汝降生之辰也。每年此日。必有以饷汝。虽家贫不能盛为酒食。而所以祝汝寿福者。岂有穷哉。而今乃以此物。酹汝祭汝。此何为耶。此何为耶。汝柩之引也。余病惫特甚。又神魂错乱。为文告汝而不尽所欲言。其后每欲更抒腷臆。而辄哀塞不能成语而止矣。今因此奠酹。略告余哀。而终亦不能尽其意也。然汝其听而飨之乎。呜呼痛哉。祭北溪李左相(世白)文(癸未)
公之气局。宏厚严峻。公之操守。廉白敬慎。垂绅正笏。百僚是镇。不声以色。纲纪自振。当大处置。举朝惊震。皆有一言。以远后衅。公独凝然。壁立千仞。何知利害。义理是顺。近时大臣。号为贤俊。及当变故。无此坚韧。勤劳王家。竟以身殉。国失元老。嗟天不慭。善类孰主。凶邪孰摈。龙亡虎逝。变怪杂进。言念世道。疾首非疢。顾弟孤露。荷公抚循。生者不愧。乃见至信。百岁之期。验公容鬓。幽明之隔。一何其迅。玄隧既启。灵輴发轫。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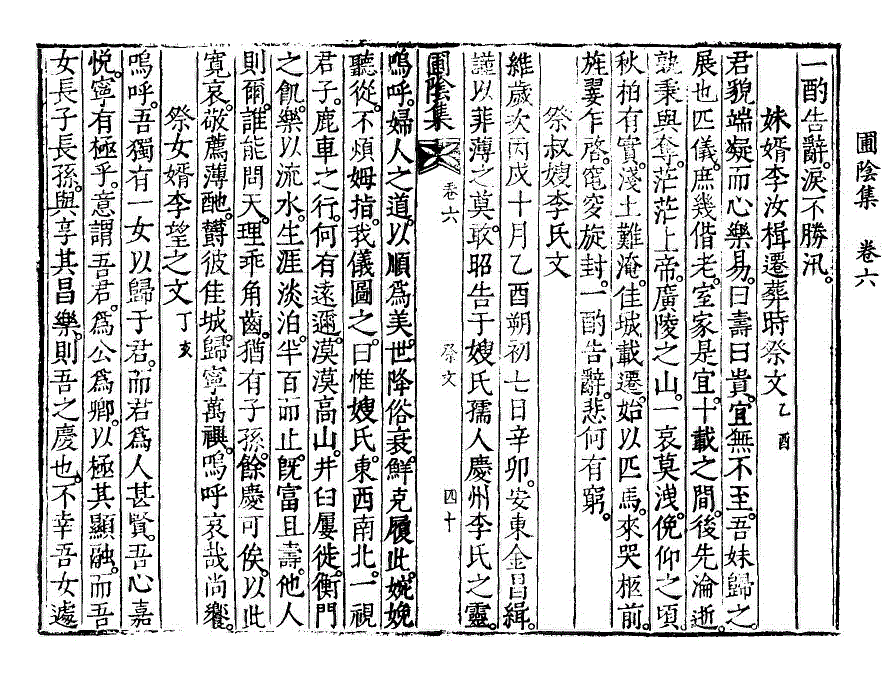 一酌告辞。泪不胜汛。
一酌告辞。泪不胜汛。妹婿李汝楫迁葬时祭文(乙酉)
君貌端凝而心乐易。曰寿曰贵。宜无不至。吾妹归之。展也匹仪。庶几偕老。室家是宜。十载之间。后先沦逝。孰秉与夺。茫茫上帝。广陵之山。一哀莫泄。俛仰之顷。秋柏有实。浅土难淹。佳城载迁。始以匹马。来哭柩前。旌翣乍启。窀穸旋封。一酌告辞。悲何有穷。
祭叔嫂李氏文
维岁次丙戌十月乙酉朔初七日辛卯。安东金昌缉。谨以菲薄之奠。敢昭告于嫂氏孺人庆州李氏之灵。呜呼。妇人之道。以顺为美。世降俗衰。鲜克履此。婉娩听从。不烦姆指。我仪图之。曰惟嫂氏。东西南北。一视君子。鹿车之行。何有远迩。漠漠高山。井臼屡徙。衡门之饥。乐以流水。生涯淡泊。半百而止。既富且寿。他人则尔。谁能问天。理乖角齿。犹有子孙。馀庆可俟。以此宽哀。敬荐薄酏。郁彼佳城。归宁万祀。呜呼哀哉尚飨。
祭女婿李望之文(丁亥)
呜呼。吾独有一女以归于君。而君为人甚贤。吾心嘉悦。宁有极乎。意谓吾君。为公为卿。以极其显融。而吾女长子长孙。与享其昌乐。则吾之庆也。不幸吾女遽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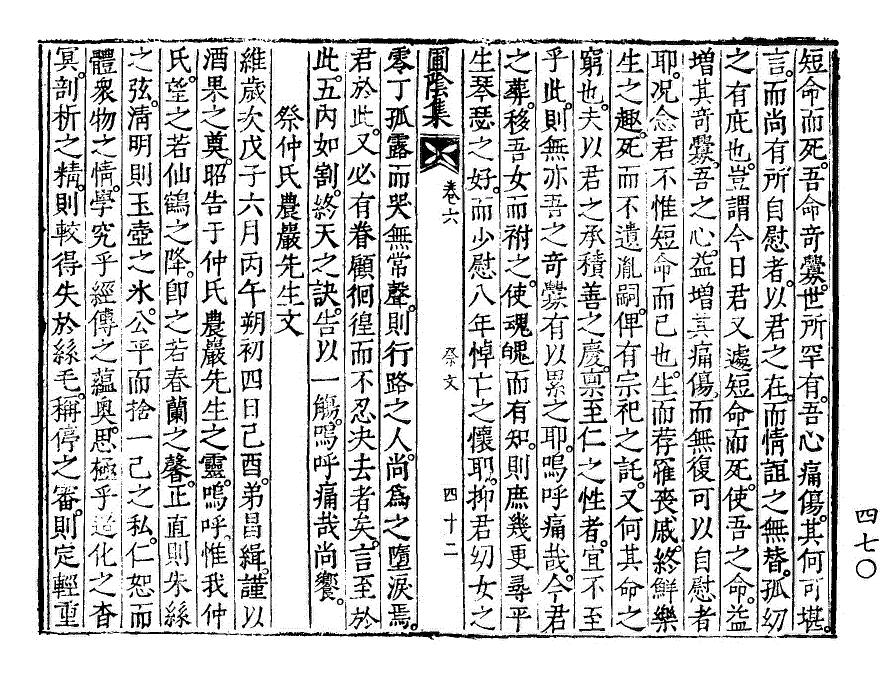 短命而死。吾命奇衅。世所罕有。吾心痛伤。其何可堪。言。而尚有所自慰者。以君之在。而情谊之无替。孤幼之有庇也。岂谓今日君又遽短命而死。使吾之命。益增其奇衅。吾之心。益增其痛伤。而无复可以自慰者耶。况念君不惟短命而已也。生而荐罹丧戚。终鲜乐生之趣。死而不遗胤嗣。俾有宗祀之托。又何其命之穷也。夫以君之承积善之庆。禀至仁之性者。宜不至乎此。则无亦吾之奇衅有以累之耶。呜呼痛哉。今君之葬。移吾女而祔之。使魂魄而有知。则庶几更寻平生琴瑟之好。而少慰八年悼亡之怀耶。抑君幼女之零丁孤露而哭无常声。则行路之人。尚为之堕泪焉。君于此。又必有眷顾徊徨而不忍决去者矣。言至于此。五内如割。终天之诀。告以一觞。呜呼痛哉尚飨。
短命而死。吾命奇衅。世所罕有。吾心痛伤。其何可堪。言。而尚有所自慰者。以君之在。而情谊之无替。孤幼之有庇也。岂谓今日君又遽短命而死。使吾之命。益增其奇衅。吾之心。益增其痛伤。而无复可以自慰者耶。况念君不惟短命而已也。生而荐罹丧戚。终鲜乐生之趣。死而不遗胤嗣。俾有宗祀之托。又何其命之穷也。夫以君之承积善之庆。禀至仁之性者。宜不至乎此。则无亦吾之奇衅有以累之耶。呜呼痛哉。今君之葬。移吾女而祔之。使魂魄而有知。则庶几更寻平生琴瑟之好。而少慰八年悼亡之怀耶。抑君幼女之零丁孤露而哭无常声。则行路之人。尚为之堕泪焉。君于此。又必有眷顾徊徨而不忍决去者矣。言至于此。五内如割。终天之诀。告以一觞。呜呼痛哉尚飨。祭仲氏农岩先生文
维岁次戊子六月丙午朔初四日己酉。弟昌缉。谨以酒果之奠。昭告于仲氏农岩先生之灵。呜呼。惟我仲氏。望之若仙鹤之降。即之若春兰之馨。正直则朱丝之弦。清明则玉壶之冰。公平而舍一己之私。仁恕而体众物之情。学究乎经传之蕴奥。思极乎造化之杳冥。剖析之精。则较得失于丝毛。称停之审。则定轻重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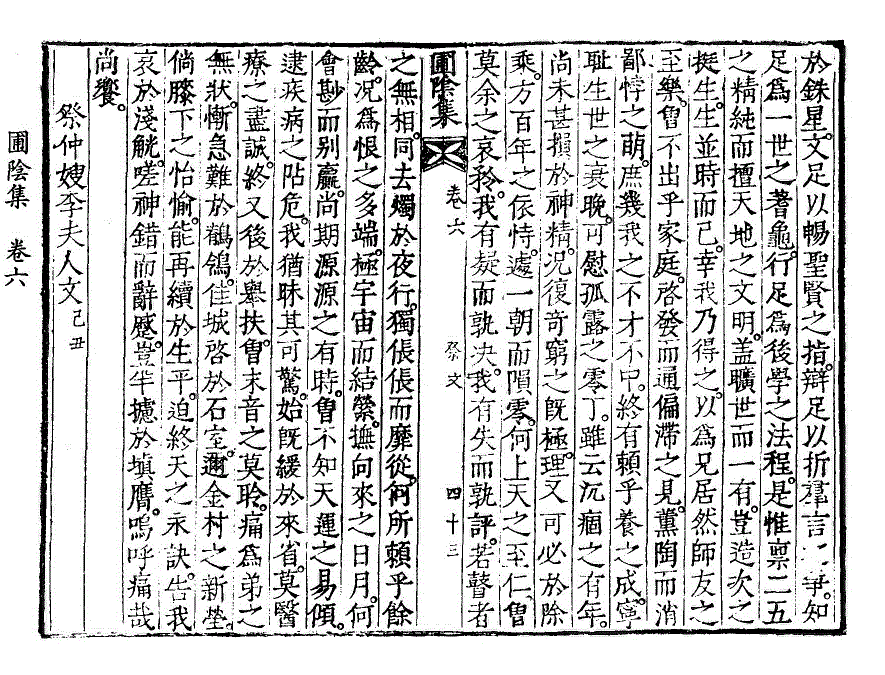 于铢星。文足以畅圣贤之指。辩足以折群言之争。知足为一世之蓍龟。行足为后学之法程。是惟禀二五之精纯而擅天地之文明。盖旷世而一有。岂造次之挺生。生并时而已。幸我乃得之。以为兄居然师友之至乐。曾不出乎家庭。启发而通偏滞之见。薰陶而消鄙悖之萌。庶几我之不才不中。终有赖乎养之成。宁耻生世之衰晚。可慰孤露之零丁。虽云沉痼之有年。尚未甚损于神精。况复奇穷之既极。理又可必于除乘。方百年之依恃。遽一朝而陨零。何上天之至仁。曾莫余之哀矜。我有疑而孰决。我有失而孰评。若瞽者之无相。同去烛于夜行。独伥伥而靡从。何所赖乎馀龄。况为恨之多端。极宇宙而结萦。抚向来之日月。何会鲜而别赢。尚期源源之有时。曾不知天运之易倾。逮疾病之阽危。我犹昧其可惊。始既缓于来省。莫医疗之尽诚。终又后于举扶。曾末音之莫聆。痛为弟之无状。惭急难于鹡鸰。佳城启于石室。迩金村之新茔。倘膝下之怡愉。能再续于生平。迫终天之永诀。告我哀于浅觥。嗟神错而辞蹙。岂半摅于填膺。呜呼痛哉尚飨。
于铢星。文足以畅圣贤之指。辩足以折群言之争。知足为一世之蓍龟。行足为后学之法程。是惟禀二五之精纯而擅天地之文明。盖旷世而一有。岂造次之挺生。生并时而已。幸我乃得之。以为兄居然师友之至乐。曾不出乎家庭。启发而通偏滞之见。薰陶而消鄙悖之萌。庶几我之不才不中。终有赖乎养之成。宁耻生世之衰晚。可慰孤露之零丁。虽云沉痼之有年。尚未甚损于神精。况复奇穷之既极。理又可必于除乘。方百年之依恃。遽一朝而陨零。何上天之至仁。曾莫余之哀矜。我有疑而孰决。我有失而孰评。若瞽者之无相。同去烛于夜行。独伥伥而靡从。何所赖乎馀龄。况为恨之多端。极宇宙而结萦。抚向来之日月。何会鲜而别赢。尚期源源之有时。曾不知天运之易倾。逮疾病之阽危。我犹昧其可惊。始既缓于来省。莫医疗之尽诚。终又后于举扶。曾末音之莫聆。痛为弟之无状。惭急难于鹡鸰。佳城启于石室。迩金村之新茔。倘膝下之怡愉。能再续于生平。迫终天之永诀。告我哀于浅觥。嗟神错而辞蹙。岂半摅于填膺。呜呼痛哉尚飨。祭仲嫂李夫人文(己丑)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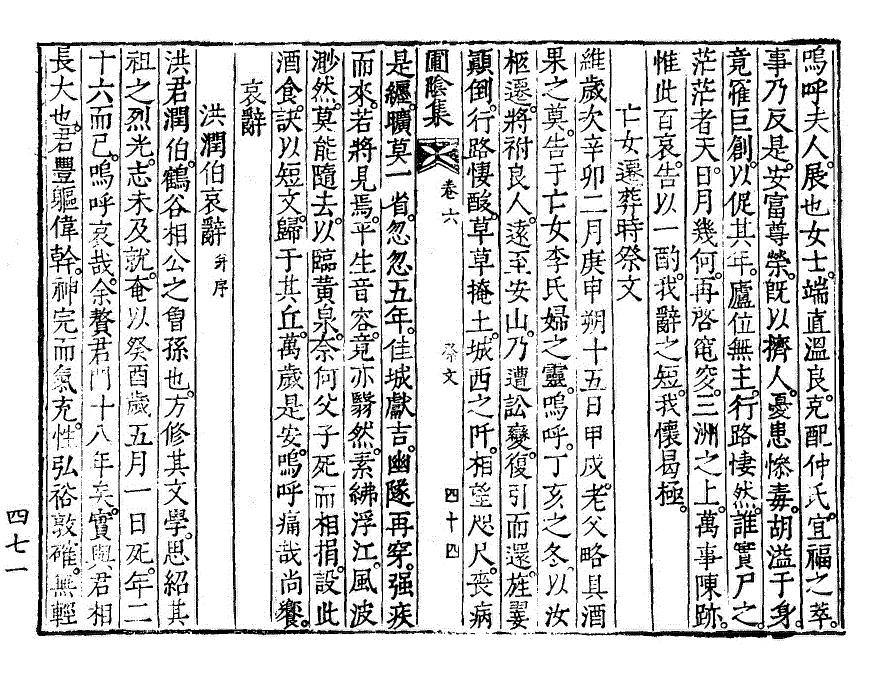 呜呼夫人。展也女士。端直温良。克配仲氏。宜福之萃。事乃反是。安富尊荣。既以挤人。忧患惨毒。胡溢于身。竟罹巨创。以促其年。庐位无主。行路悽然。谁实尸之。茫茫者天。日月几何。再启窀穸。三洲之上。万事陈迹。惟此百哀。告以一酌。我辞之短。我怀曷极。
呜呼夫人。展也女士。端直温良。克配仲氏。宜福之萃。事乃反是。安富尊荣。既以挤人。忧患惨毒。胡溢于身。竟罹巨创。以促其年。庐位无主。行路悽然。谁实尸之。茫茫者天。日月几何。再启窀穸。三洲之上。万事陈迹。惟此百哀。告以一酌。我辞之短。我怀曷极。亡女迁葬时祭文
维岁次辛卯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甲戌。老父略具酒果之奠。告于亡女李氏妇之灵。呜呼。丁亥之冬。以汝柩迁。将祔良人。远至安山。乃遭讼变。复引而还。旌翣颠倒。行路悽酸。草草掩土。城西之阡。相望咫尺。丧病是缠。旷莫一省。忽忽五年。佳城献吉。幽隧再穿。强疾而来。若将见焉。平生音容。竟亦翳然。素绋浮江。风波渺然。莫能随去。以临黄泉。奈何父子死而相捐。设此酒食。诀以短文。归于其丘。万岁是安。呜呼痛哉尚飨。
圃阴集卷之六(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哀辞
洪润伯哀辞(并序)
洪君润伯。鹤谷相公之曾孙也。方修其文学。思绍其祖之烈光。志未及就。奄以癸酉岁五月一日死。年二十六而已。呜呼哀哉。余赘君门十八年矣。实与君相长大也。君丰躯伟干。神完而气充。性弘裕敦确。无轻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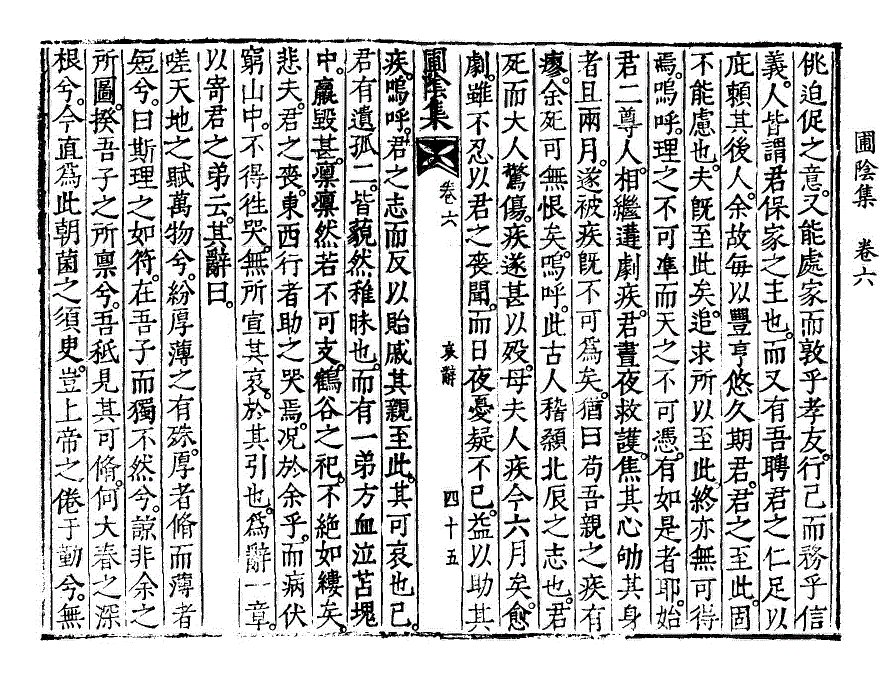 佻迫促之意。又能处家而敦乎孝友。行己而务乎信义。人皆谓君保家之主也。而又有吾聘君之仁足以庇赖其后人。余故每以丰亨悠久期君。君之至此。固不能虑也。夫既至此矣。追求所以至此。终亦无可得焉。呜呼。理之不可准而天之不可凭。有如是者耶。始君二尊人。相继遘剧疾。君昼夜救护。焦其心劬其身者且两月。遂被疾既不可为矣。犹曰苟吾亲之疾有瘳。余死可无恨矣。呜呼。此古人稽颡北辰之志也。君死而大人惊伤。疾遂甚以殁。母夫人疾今六月矣。愈剧。虽不忍以君之丧闻。而日夜忧疑不已。益以助其疾。呜呼。君之志而反以贻戚其亲至此。其可哀也已。君有遗孤二。皆藐然稚昧也。而有一弟方血泣苫块中。羸毁甚。凛凛然若不可支。鹤谷之祀。不绝如缕矣。悲夫。君之丧。东西行者助之哭焉。况于余乎。而病伏穷山中。不得往哭。无所宣其哀。于其引也。为辞一章。以寄君之弟云。其辞曰。
佻迫促之意。又能处家而敦乎孝友。行己而务乎信义。人皆谓君保家之主也。而又有吾聘君之仁足以庇赖其后人。余故每以丰亨悠久期君。君之至此。固不能虑也。夫既至此矣。追求所以至此。终亦无可得焉。呜呼。理之不可准而天之不可凭。有如是者耶。始君二尊人。相继遘剧疾。君昼夜救护。焦其心劬其身者且两月。遂被疾既不可为矣。犹曰苟吾亲之疾有瘳。余死可无恨矣。呜呼。此古人稽颡北辰之志也。君死而大人惊伤。疾遂甚以殁。母夫人疾今六月矣。愈剧。虽不忍以君之丧闻。而日夜忧疑不已。益以助其疾。呜呼。君之志而反以贻戚其亲至此。其可哀也已。君有遗孤二。皆藐然稚昧也。而有一弟方血泣苫块中。羸毁甚。凛凛然若不可支。鹤谷之祀。不绝如缕矣。悲夫。君之丧。东西行者助之哭焉。况于余乎。而病伏穷山中。不得往哭。无所宣其哀。于其引也。为辞一章。以寄君之弟云。其辞曰。嗟天地之赋万物兮。纷厚薄之有殊。厚者脩而薄者短兮。曰斯理之如符。在吾子而独不然兮。谅非余之所图。揆吾子之所禀兮。吾秪见其可脩。何大春之深根兮。今直为此朝菌之须臾。岂上帝之倦于勤兮。无
圃阴集卷之六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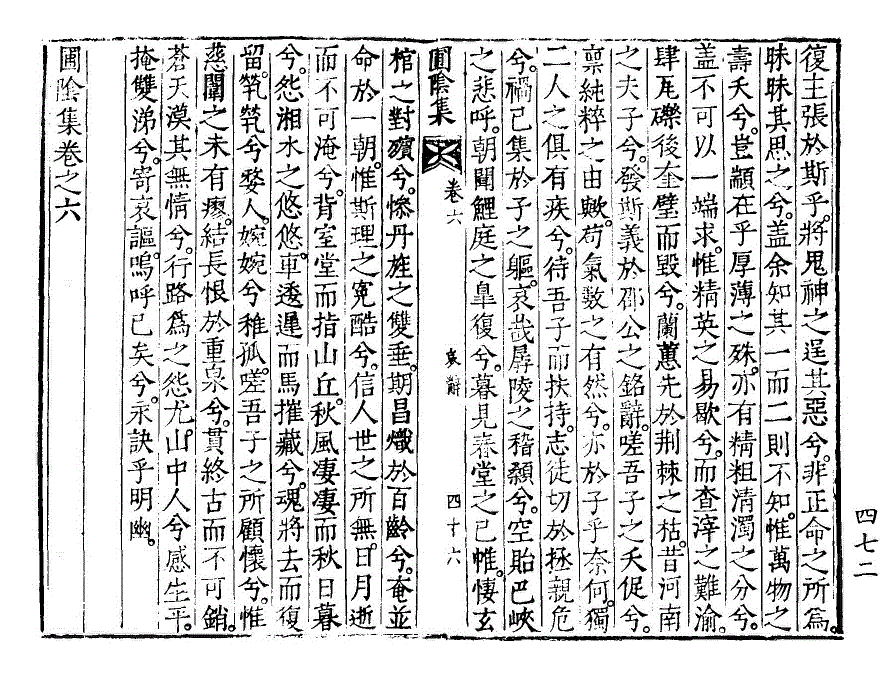 复主张于斯乎。将鬼神之逞其恶兮。非正命之所为。昧昧其思之兮。盖余知其一而二则不知。惟万物之寿夭兮。岂颛在乎厚薄之殊。亦有精粗清浊之分兮。盖不可以一端求。惟精英之易歇兮。而查滓之难渝。肆瓦砾后奎璧而毁兮。兰蕙先于荆棘之枯。昔河南之夫子兮。发斯义于邵公之铭辞。嗟吾子之夭促兮。禀纯粹之由欤。苟气数之有然兮。亦于子乎奈何。独二人之俱有疾兮。待吾子而扶持。志徒切于拯亲危兮。祸已集于子之躯。哀哉孱陵之稽颡兮。空贻巴峡之悲呼。朝闻鲤庭之皋复兮。暮见春堂之已帷。悽玄棺之对殡兮。惨丹旌之双垂。期昌炽于百龄兮。奄并命于一朝。惟斯理之冤酷兮。信人世之所无。日月逝而不可淹兮。背室堂而指山丘。秋风凄凄而秋日暮兮。怨湘水之悠悠。车逶迟而马摧藏兮。魂将去而复留。茕茕兮嫠人。婉婉兮稚孤。嗟吾子之所顾怀兮。惟慈闱之未有瘳。结长恨于重泉兮。贯终古而不可销。苍天漠其无情兮。行路为之怨尤。山中人兮感生平。掩双涕兮。寄哀讴。呜呼已矣兮。永诀乎明幽。
复主张于斯乎。将鬼神之逞其恶兮。非正命之所为。昧昧其思之兮。盖余知其一而二则不知。惟万物之寿夭兮。岂颛在乎厚薄之殊。亦有精粗清浊之分兮。盖不可以一端求。惟精英之易歇兮。而查滓之难渝。肆瓦砾后奎璧而毁兮。兰蕙先于荆棘之枯。昔河南之夫子兮。发斯义于邵公之铭辞。嗟吾子之夭促兮。禀纯粹之由欤。苟气数之有然兮。亦于子乎奈何。独二人之俱有疾兮。待吾子而扶持。志徒切于拯亲危兮。祸已集于子之躯。哀哉孱陵之稽颡兮。空贻巴峡之悲呼。朝闻鲤庭之皋复兮。暮见春堂之已帷。悽玄棺之对殡兮。惨丹旌之双垂。期昌炽于百龄兮。奄并命于一朝。惟斯理之冤酷兮。信人世之所无。日月逝而不可淹兮。背室堂而指山丘。秋风凄凄而秋日暮兮。怨湘水之悠悠。车逶迟而马摧藏兮。魂将去而复留。茕茕兮嫠人。婉婉兮稚孤。嗟吾子之所顾怀兮。惟慈闱之未有瘳。结长恨于重泉兮。贯终古而不可销。苍天漠其无情兮。行路为之怨尤。山中人兮感生平。掩双涕兮。寄哀讴。呜呼已矣兮。永诀乎明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