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杂著
杂著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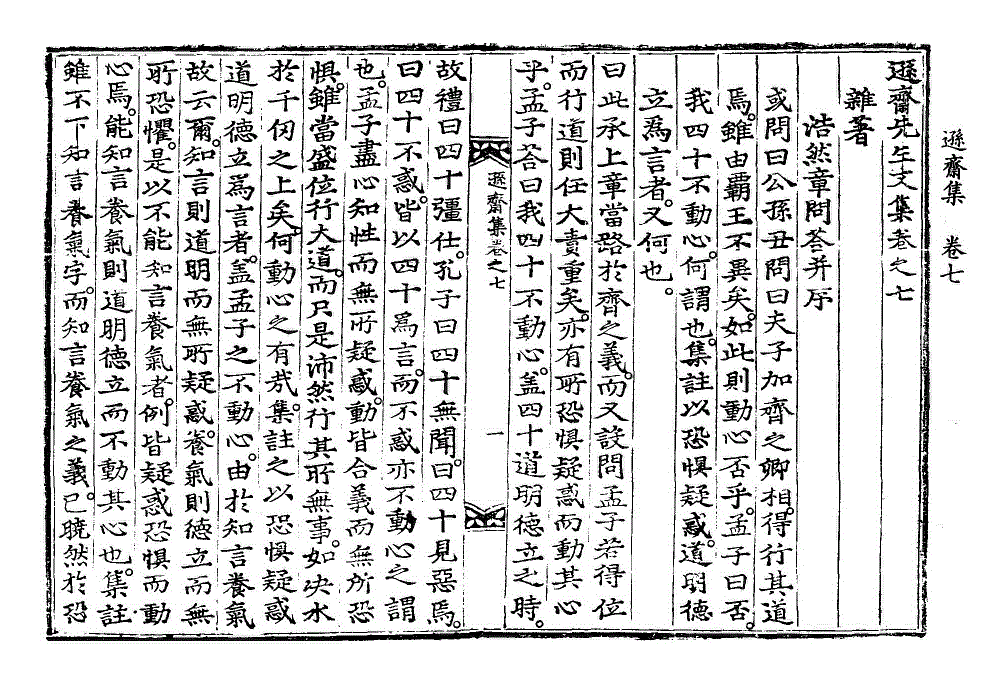 浩然章问答(并序)
浩然章问答(并序)或问曰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其道焉。虽由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何谓也。集注以恐惧疑惑。道明德立为言者。又何也。
曰此承上章当路于齐之义。而又设问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则任大责重矣。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孟子答曰我四十不动心。盖四十道明德立之时。故礼曰四十彊仕。孔子曰四十无闻。曰四十见恶焉。曰四十不惑。皆以四十为言。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也。孟子尽心知性而无所疑惑。动皆合义而无所恐惧。虽当盛位行大道。而只是沛然行其所无事。如决水于千仞之上矣。何动心之有哉。集注之以恐惧疑惑道明德立为言者。盖孟子之不动心。由于知言养气故云尔。知言则道明而无所疑惑。养气则德立而无所恐惧。是以不能知言养气者。例皆疑惑恐惧而动心焉。能知言养气则道明德立而不动其心也。集注虽不下知言养气字。而知言养气之义。已晓然于恐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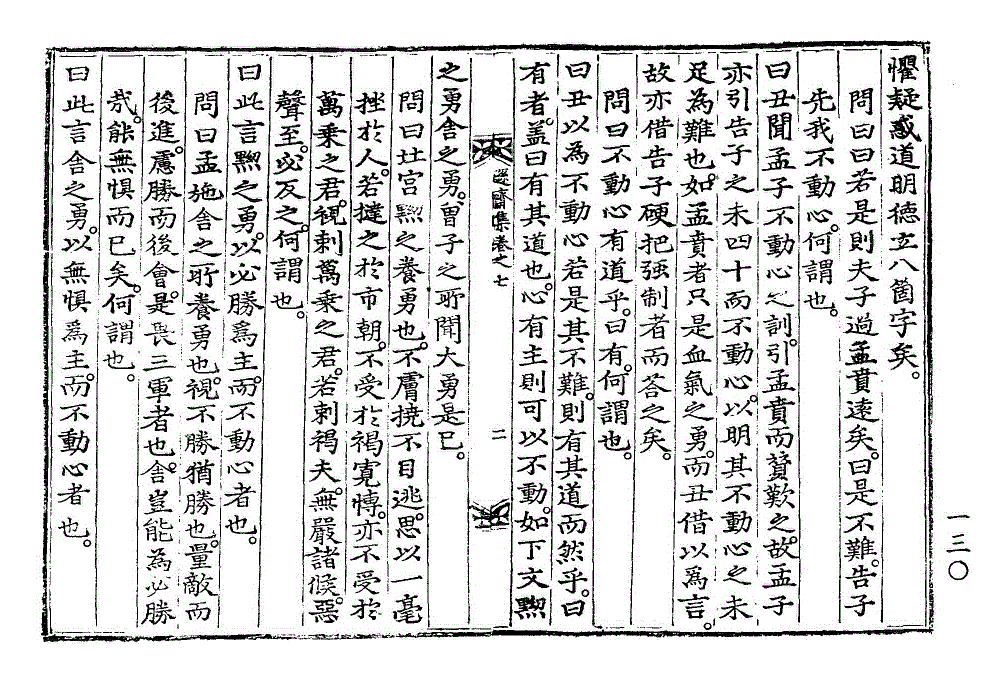 惧疑惑道明德立八个字矣。
惧疑惑道明德立八个字矣。问曰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何谓也。
曰丑闻孟子不动心之训。引孟贲而赞叹之。故孟子亦引告子之未四十而不动心。以明其不动心之未足为难也。如孟贲者只是血气之勇。而丑借以为言。故亦借告子硬把强制者而答之矣。
问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何谓也。
曰丑以为不动心若是其不难。则有其道而然乎。曰有者。盖曰有其道也。心有主则可以不动。如下文黝之勇舍之勇。曾子之所闻大勇是已。
问曰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何谓也。
曰此言黝之勇。以必胜为主。而不动心者也。
问曰孟施舍之所养勇也。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何谓也。
曰此言舍之勇。以无惧为主。而不动心者也。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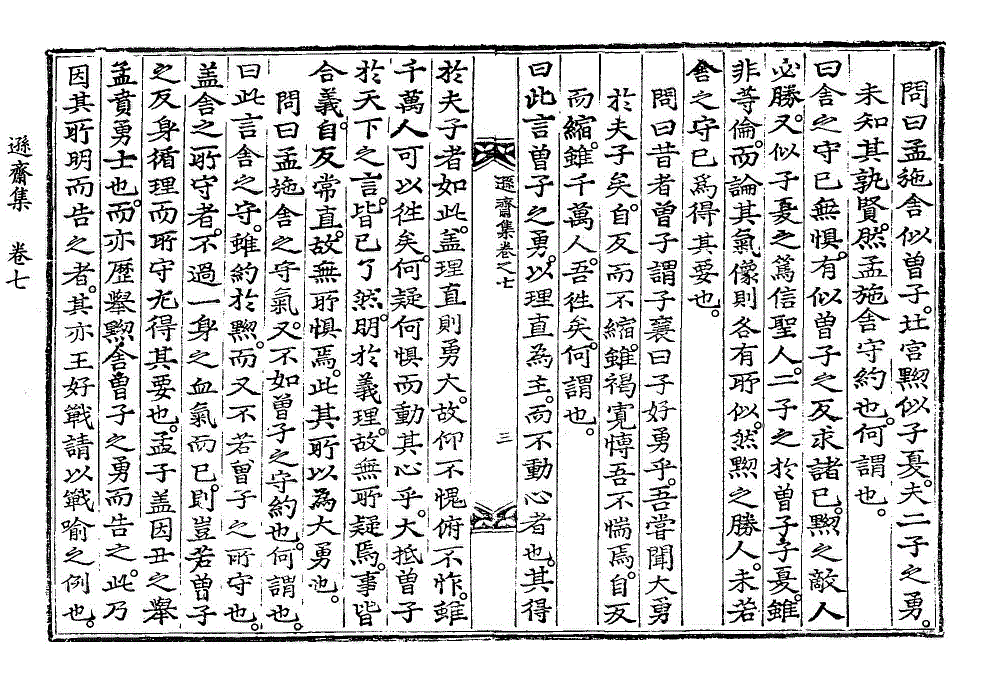 问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孟施舍守约也。何谓也。
问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孟施舍守约也。何谓也。曰舍之守己无惧。有似曾子之反求诸己。黝之敌人必胜。又似子夏之笃信圣人。二子之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而论其气像则各有所似。然黝之胜人。未若舍之守己为得其要也。
问曰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何谓也。
曰此言曾子之勇。以理直为主。而不动心者也。其得于夫子者如此。盖理直则勇大。故仰不愧俯不怍。虽千万人可以往矣。何疑何惧而动其心乎。大抵曾子于天下之言。皆已了然。明于义理。故无所疑焉。事皆合义。自反常直。故无所惧焉。此其所以为大勇也。
问曰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何谓也。
曰此言舍之守。虽约于黝。而又不若曾子之所守也。盖舍之所守者。不过一身之血气而已。则岂若曾子之反身循理而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盖因丑之举孟贲勇士也。而亦历举黝,舍,曾子之勇而告之。此乃因其所明而告之者。其亦王好战请以战喻之例也。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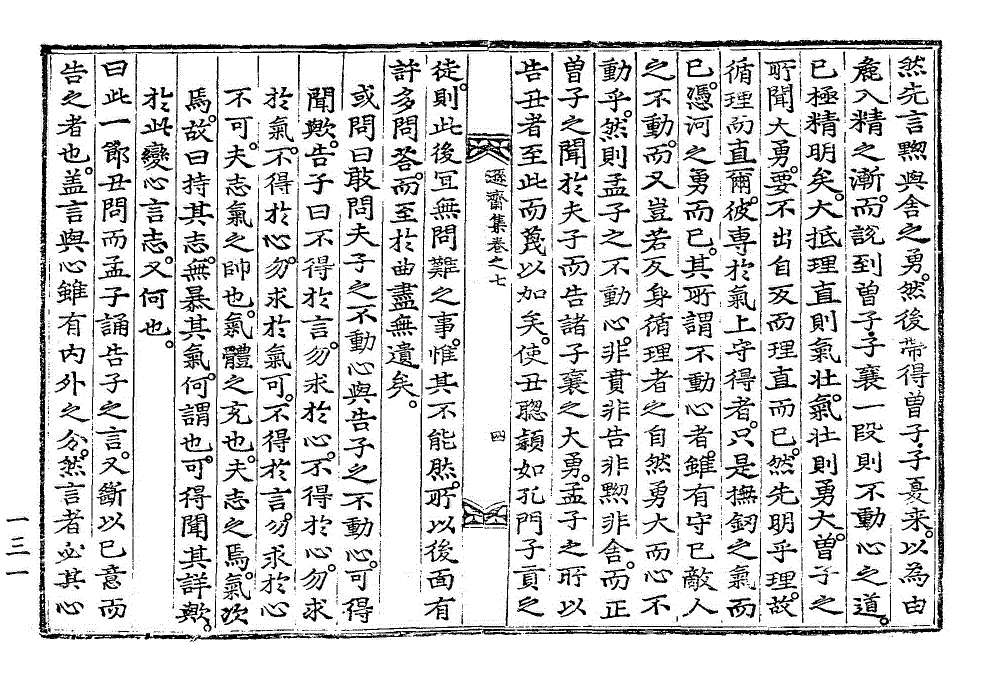 然先言黝与舍之勇。然后带得曾子,子夏来。以为由粗入精之渐。而说到曾子,子襄一段则不动心之道。已极精明矣。大抵理直则气壮。气壮则勇大。曾子之所闻大勇。要不出自反而理直而已。然先明乎理。故循理而直尔。彼专于气上守得者。只是抚釖之气而已。凭河之勇而已。其所谓不动心者。虽有守己敌人之不动。而又岂若反身循理者之自然勇大而心不动乎。然则孟子之不动心。非贲非告非黝非舍。而正曾子之闻于夫子而告诸子襄之大勇。孟子之所以告丑者至此而蔑以加矣。使丑聪颖如孔门子贡之徒。则此后宜无问难之事。惟其不能然。所以后面有许多问答。而至于曲尽无遗矣。
然先言黝与舍之勇。然后带得曾子,子夏来。以为由粗入精之渐。而说到曾子,子襄一段则不动心之道。已极精明矣。大抵理直则气壮。气壮则勇大。曾子之所闻大勇。要不出自反而理直而已。然先明乎理。故循理而直尔。彼专于气上守得者。只是抚釖之气而已。凭河之勇而已。其所谓不动心者。虽有守己敌人之不动。而又岂若反身循理者之自然勇大而心不动乎。然则孟子之不动心。非贲非告非黝非舍。而正曾子之闻于夫子而告诸子襄之大勇。孟子之所以告丑者至此而蔑以加矣。使丑聪颖如孔门子贡之徒。则此后宜无问难之事。惟其不能然。所以后面有许多问答。而至于曲尽无遗矣。或问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欤。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之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谓也。可得闻其详欤。于此变心言志。又何也。
曰此一节丑问而孟子诵告子之言。又断以己意而告之者也。盖言与心虽有内外之分。然言者必其心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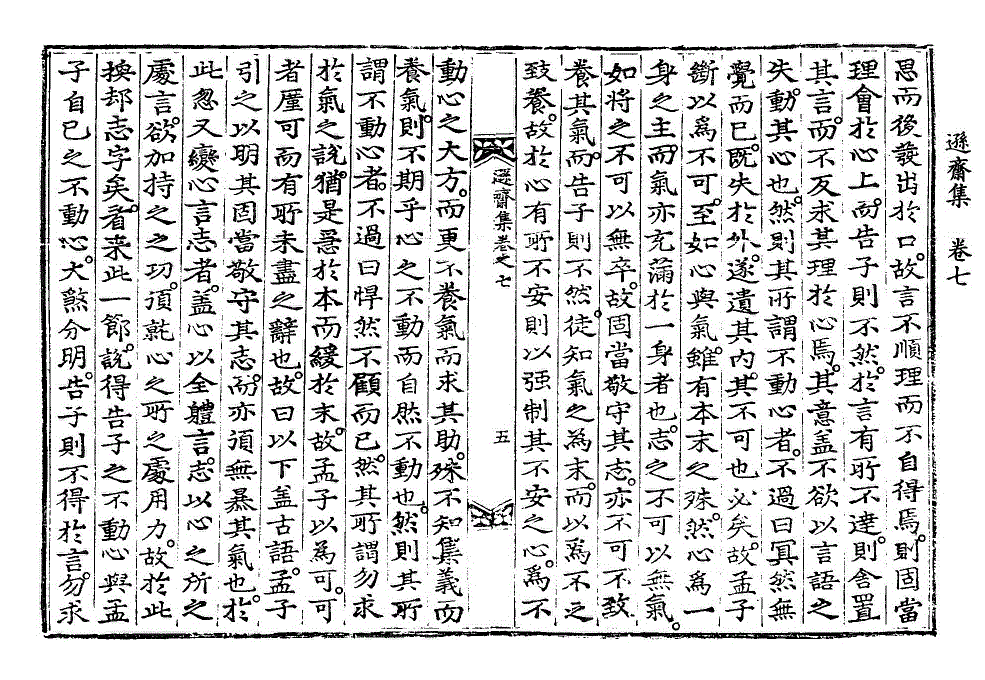 思而后发出于口。故言不顺理而不自得焉。则固当理会于心上。而告子则不然。于言有所不达。则舍置其言。而不反求其理于心焉。其意盖不欲以言语之失。动其心也。然则其所谓不动心者。不过曰冥然无觉而已。既失于外。遂遗其内。其不可也必矣。故孟子断以为不可。至如心与气。虽有本末之殊。然心为一身之主。而气亦充满于一身者也。志之不可以无气。如将之不可以无卒。故固当敬守其志。亦不可不致养其气。而告子则不然。徒知气之为末。而以为不之致养。故于心有所不安则以强制其不安之心。为不动心之大方。而更不养气而求其助。殊不知集义而养气。则不期乎心之不动而自然不动也。然则其所谓不动心者。不过曰悍然不顾而已。然其所谓勿求于气之说。犹是急于本而缓于末。故孟子以为可。可者廑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故曰以下盖古语。孟子引之以明其固当敬守其志。而亦须无暴其气也。于此忽又变心言志者。盖心以全体言。志以心之所之处言。欲加持之之功。须就心之所之处用力。故于此换却志字矣。看来此一节。说得告子之不动心与孟子自己之不动心。大煞分明。告子则不得于言。勿求
思而后发出于口。故言不顺理而不自得焉。则固当理会于心上。而告子则不然。于言有所不达。则舍置其言。而不反求其理于心焉。其意盖不欲以言语之失。动其心也。然则其所谓不动心者。不过曰冥然无觉而已。既失于外。遂遗其内。其不可也必矣。故孟子断以为不可。至如心与气。虽有本末之殊。然心为一身之主。而气亦充满于一身者也。志之不可以无气。如将之不可以无卒。故固当敬守其志。亦不可不致养其气。而告子则不然。徒知气之为末。而以为不之致养。故于心有所不安则以强制其不安之心。为不动心之大方。而更不养气而求其助。殊不知集义而养气。则不期乎心之不动而自然不动也。然则其所谓不动心者。不过曰悍然不顾而已。然其所谓勿求于气之说。犹是急于本而缓于末。故孟子以为可。可者廑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故曰以下盖古语。孟子引之以明其固当敬守其志。而亦须无暴其气也。于此忽又变心言志者。盖心以全体言。志以心之所之处言。欲加持之之功。须就心之所之处用力。故于此换却志字矣。看来此一节。说得告子之不动心与孟子自己之不动心。大煞分明。告子则不得于言。勿求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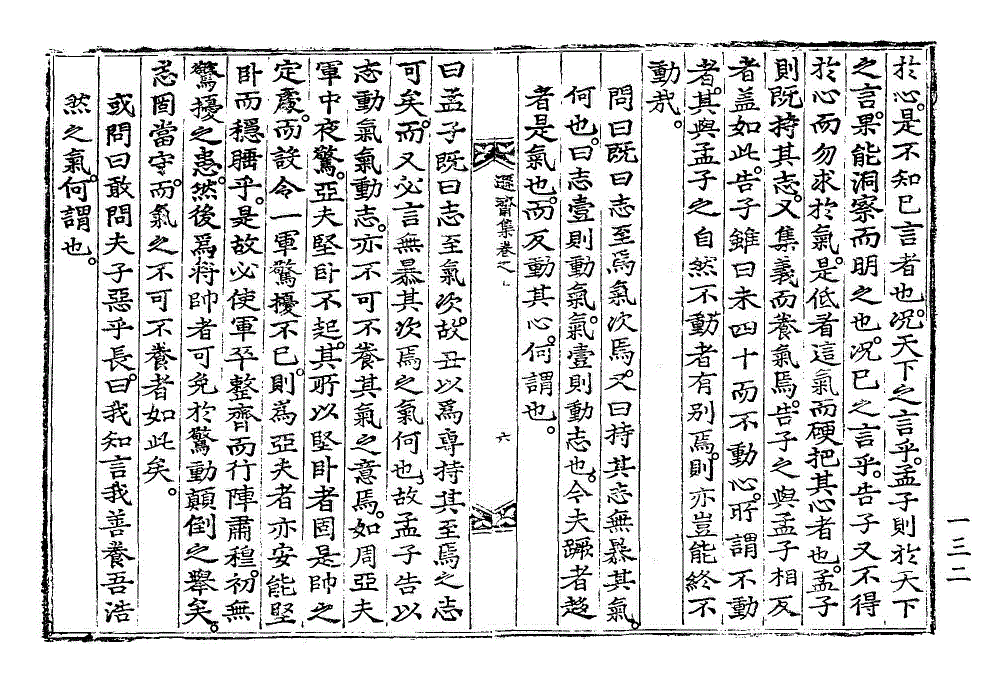 于心。是不知己言者也。况天下之言乎。孟子则于天下之言。果能洞察而明之也。况己之言乎。告子又不得于心而勿求于气。是低看这气而硬把其心者也。孟子则既持其志。又集义而养气焉。告子之与孟子相反者盖如此。告子虽曰未四十而不动心。所谓不动者。其与孟子之自然不动者有别焉。则亦岂能终不动哉。
于心。是不知己言者也。况天下之言乎。孟子则于天下之言。果能洞察而明之也。况己之言乎。告子又不得于心而勿求于气。是低看这气而硬把其心者也。孟子则既持其志。又集义而养气焉。告子之与孟子相反者盖如此。告子虽曰未四十而不动心。所谓不动者。其与孟子之自然不动者有别焉。则亦岂能终不动哉。问曰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趍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何谓也。
曰孟子既曰志至气次。故丑以为专持其至焉之志可矣。而又必言无暴其次焉之气何也。故孟子告以志动气气动志。亦不可不养其气之意焉。如周亚夫军中夜惊。亚夫坚卧不起。其所以坚卧者固是帅之定处。而设令一军惊扰不已。则为亚夫者亦安能坚卧而稳睡乎。是故必使军卒整齐而行阵肃穆。初无惊扰之患。然后为将帅者可免于惊动颠倒之举矣。志固当守。而气之不可不养者如此矣。
或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也。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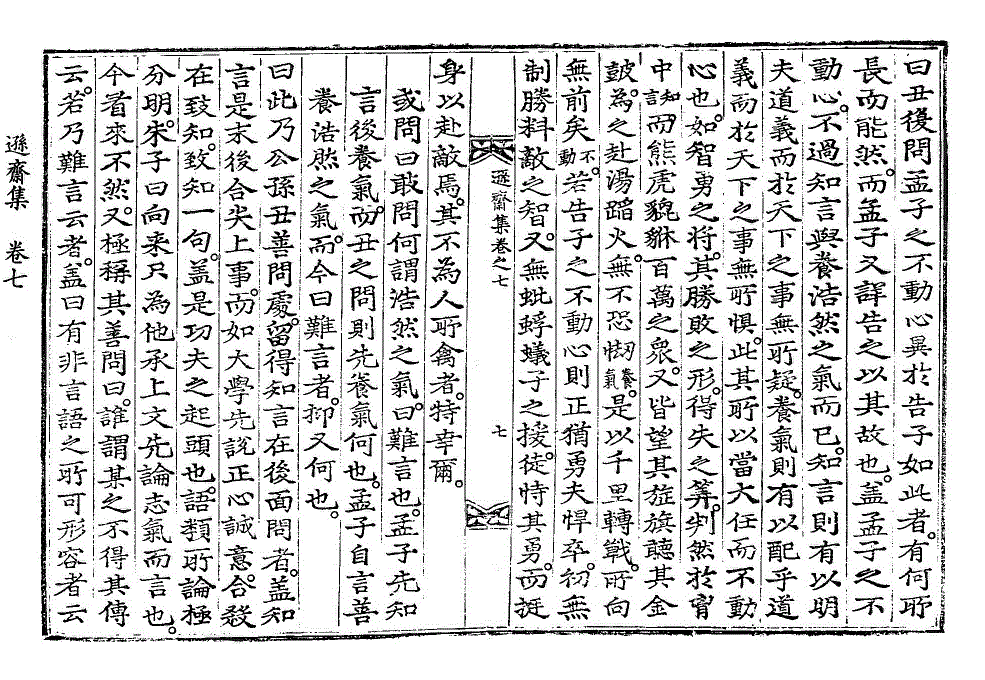 曰丑复问孟子之不动心异于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长而能然。而孟子又详告之以其故也。盖孟子之不动心。不过知言与养浩然之气而已。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乎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如智勇之将。其胜败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中(知言)。而熊虎貔貅百万之众。又皆望其旌旗听其金鼓。为之赴汤蹈火。无不恐㥘(养气)。是以千里转战。所向无前矣(不动)。若告子之不动心则正犹勇夫悍卒。初无制胜料敌之智。又无蚍蜉蚁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敌焉。其不为人所禽者。特幸尔。
曰丑复问孟子之不动心异于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长而能然。而孟子又详告之以其故也。盖孟子之不动心。不过知言与养浩然之气而已。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乎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如智勇之将。其胜败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中(知言)。而熊虎貔貅百万之众。又皆望其旌旗听其金鼓。为之赴汤蹈火。无不恐㥘(养气)。是以千里转战。所向无前矣(不动)。若告子之不动心则正犹勇夫悍卒。初无制胜料敌之智。又无蚍蜉蚁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敌焉。其不为人所禽者。特幸尔。或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孟子先知言后养气。而丑之问则先养气何也。孟子自言善养浩然之气。而今曰难言者。抑又何也。
曰此乃公孙丑善问处。留得知言在后面问者。盖知言是末后合尖上事。而如大学先说正心诚意。合杀在致知。致知一句。盖是功夫之起头也。语类所论极分明。朱子曰向来只为他承上文先论志气而言也。今看来不然。又极称其善问曰。谁谓某之不得其传云。若乃难言云者。盖曰有非言语之所可形容者云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3L 页
 尔。观于此可见孟子之实有是气也。若未有是气则亦岂知难言气像也。
尔。观于此可见孟子之实有是气也。若未有是气则亦岂知难言气像也。问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何谓也。
曰浩然之为气也。语其体段则至大而无限量。至刚而不可屈。盖是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其为体段。本自如是。苟能循乎义理而自反常直。无害其本来体段。则充塞弥满于天地之间矣。此段直字。与曾子缩字义一般。塞于天地。亦千万人吾往意思尔。
问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何谓也。吕子约无道义则气馁之说如何。
曰浩然之为气也。语其功用则配乎道义也。盖道与义。是无形无为之理。而浩然之气。合而为之助焉。所以行之勇决。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之势。夫何疑何惮焉。若无此浩然之气。则如沟渎无源之水。断了又断尔。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体有不充。只是薾然衰飒底人也。有疑有惧。不足以有为矣。若夫吕氏之见则朱夫子攻斥之言。不啻明白。今不必更赘。而窃详孟子本文之义。上文则言浩气之体段本自刚大。果能直养无害则充体而塞天地。此段则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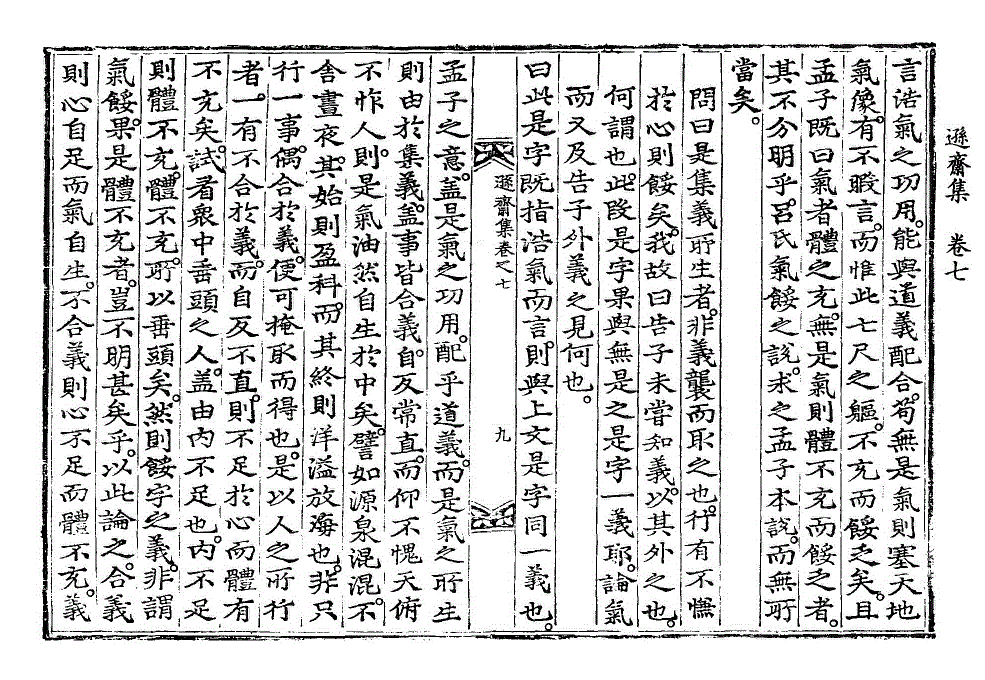 言浩气之功用。能与道义配合。苟无是气则塞天地气像。有不暇言。而惟此七尺之躯。不充而馁乏矣。且孟子既曰气者体之充。无是气则体不充而馁乏者。其不分明乎。吕氏气馁之说。求之孟子本说。而无所当矣。
言浩气之功用。能与道义配合。苟无是气则塞天地气像。有不暇言。而惟此七尺之躯。不充而馁乏矣。且孟子既曰气者体之充。无是气则体不充而馁乏者。其不分明乎。吕氏气馁之说。求之孟子本说。而无所当矣。问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何谓也。此段是字果与无是之是字一义耶。论气而又及告子外义之见何也。
曰此是字既指浩气而言。则与上文是字同一义也。孟子之意。盖是气之功用。配乎道义。而是气之所生则由于集义。盖事皆合义。自反常直。而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则是气油然自生于中矣。譬如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其始则盈科。而其终则洋溢放海也。非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取而得也。是以人之所行者。一有不合于义。而自反不直。则不足于心而体有不充矣。试看众中垂头之人。盖由内不足也。内不足则体不充。体不充。所以垂头矣。然则馁字之义。非谓气馁。果是体不充者。岂不明甚矣乎。以此论之。合义则心自足而气自生。不合义则心不足而体不充。义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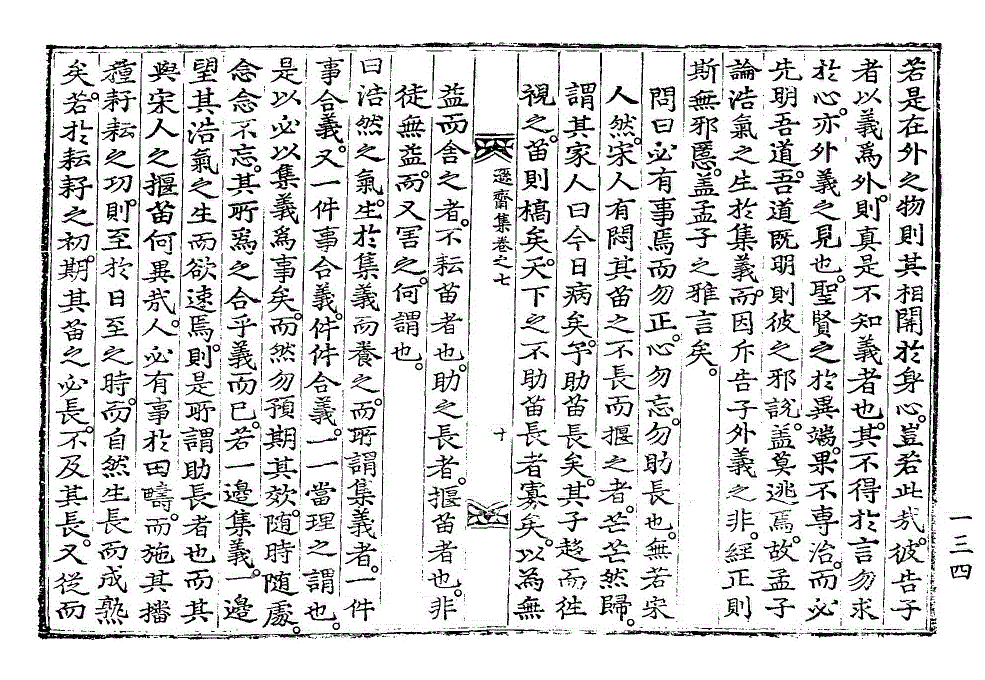 若是在外之物则其相关于身心。岂若此哉。彼告子者以义为外。则真是不知义者也。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亦外义之见也。圣贤之于异端。果不专治。而必先明吾道。吾道既明则彼之邪说。盖莫逃焉。故孟子论浩气之生于集义。而因斥告子外义之非。经正则斯无邪慝。盖孟子之雅言矣。
若是在外之物则其相关于身心。岂若此哉。彼告子者以义为外。则真是不知义者也。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亦外义之见也。圣贤之于异端。果不专治。而必先明吾道。吾道既明则彼之邪说。盖莫逃焉。故孟子论浩气之生于集义。而因斥告子外义之非。经正则斯无邪慝。盖孟子之雅言矣。问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闷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趍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也。
曰浩然之气。生于集义而养之。而所谓集义者。一件事合义。又一件事合义。件件合义。一一当理之谓也。是以必以集义为事矣。而然勿预期其效。随时随处。念念不忘。其所为之合乎义而已。若一边集义。一边望其浩气之生而欲速焉。则是所谓助长者也而其与宋人之揠苗何异哉。人必有事于田畴。而施其播种耔耘之功。则至于日至之时。而自然生长而成熟矣。若于耘耔之初。期其苗之必长。不及其长。又从而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5H 页
 拔之焉。则其为逆天也甚矣。适所以害其苗而已。彼以养气为无益。而初不用功于集义者。不耘苗者也。虽有所事而期待欲速。乃揠苗者也。然则助长之害。反有甚于不耘者矣。
拔之焉。则其为逆天也甚矣。适所以害其苗而已。彼以养气为无益。而初不用功于集义者。不耘苗者也。虽有所事而期待欲速。乃揠苗者也。然则助长之害。反有甚于不耘者矣。或问曰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何谓也。
曰心有蔽陷离穷之失。则言必有诐淫邪遁之病。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非心通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者。不能也。不能然者。其于王霸邪正公私义理是非善恶。未能了然明白矣。顾何能居盛位临大事。一一判决而无惑也。大学之格致诚正。论语之博文约礼。中庸之明善诚身。易所谓穷理尽性。今孟子所谓知言养气。槩乎皆以知为先者。岂无所以也。异端之言。一切反是。莫不有诐淫邪遁之病。如告子者不得于言而不肯求之于心。至为义外之说。则自不免于四者之病。其何能知天下之言而无所疑哉。
问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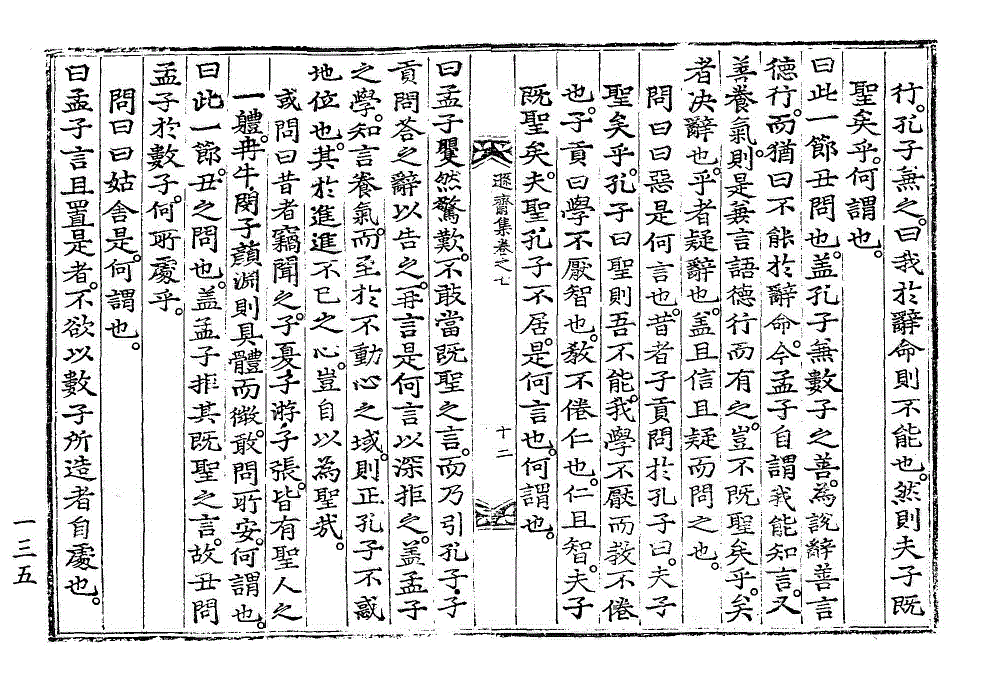 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何谓也。
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何谓也。曰此一节丑问也。盖孔子兼数子之善。为说辞善言德行。而犹曰不能于辞命。今孟子自谓我能知言。又善养气。则是兼言语德行而有之。岂不既圣矣乎。矣者决辞也。乎者疑辞也。盖且信且疑而问之也。
问曰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何谓也。
曰孟子矍然惊叹。不敢当既圣之言。而乃引孔子,子贡问答之辞以告之。再言是何言以深拒之。盖孟子之学。知言养气。而至于不动心之域。则正孔子不惑地位也。其于进进不已之心。岂自以为圣哉。
或问曰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何谓也。
曰此一节。丑之问也。盖孟子拒其既圣之言。故丑问孟子于数子。何所处乎。
问曰曰姑舍是。何谓也。
曰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数子所造者自处也。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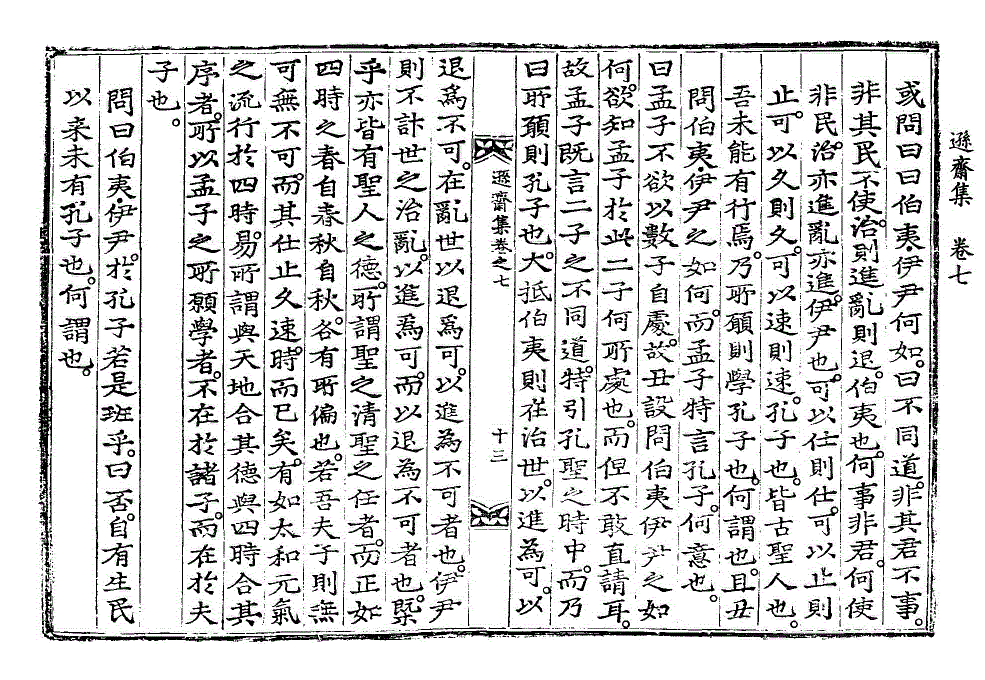 或问曰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何谓也。且丑问伯夷,伊尹之如何。而孟子特言孔子。何意也。
或问曰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何谓也。且丑问伯夷,伊尹之如何。而孟子特言孔子。何意也。曰孟子不欲以数子自处。故丑设问伯夷,伊尹之如何。欲知孟子于此二子何所处也。而但不敢直请耳。故孟子既言二子之不同道。特引孔圣之时中。而乃曰所愿则孔子也。大抵伯夷则在治世。以进为可。以退为不可。在乱世以退为可。以进为不可者也。伊尹则不计世之治乱。以进为可。而以退为不可者也。槩乎亦皆有圣人之德。所谓圣之清圣之任者。而正如四时之春自春秋自秋。各有所偏也。若吾夫子则无可无不可。而其仕止久速。时而已矣。有如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易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者。所以孟子之所愿学者。不在于诸子。而在于夫子也。
问曰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何谓也。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6L 页
 曰孟子以皆古圣人为言。故丑疑其齐等而问之。而孟子答以不同矣。
曰孟子以皆古圣人为言。故丑疑其齐等而问之。而孟子答以不同矣。问曰曰然则有同欤。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何谓也。
曰孟子言不同之截然。故丑问其亦有所同者。而孟子答以有同。盖百里可王。德之盛也。有所不为。心之正也。惟其德之盛心之正。大本大节则同也。然此一节。收煞得一章大旨。百里可王则任大责重而不动心之义在焉。一不义不为则事皆合义而有浩然之气可知矣。圣贤之言。意在言表者盖如此。
问曰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何谓也。
曰丑又问所异者如何。故孟子将引宰我,子贡,有若之言以證之。而先言三子智足以知圣人。以明其言之为可信也。
问曰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何谓也。
曰尧舜治天下于一时。夫子又推明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得夫子而明焉。则其功反有贤于尧舜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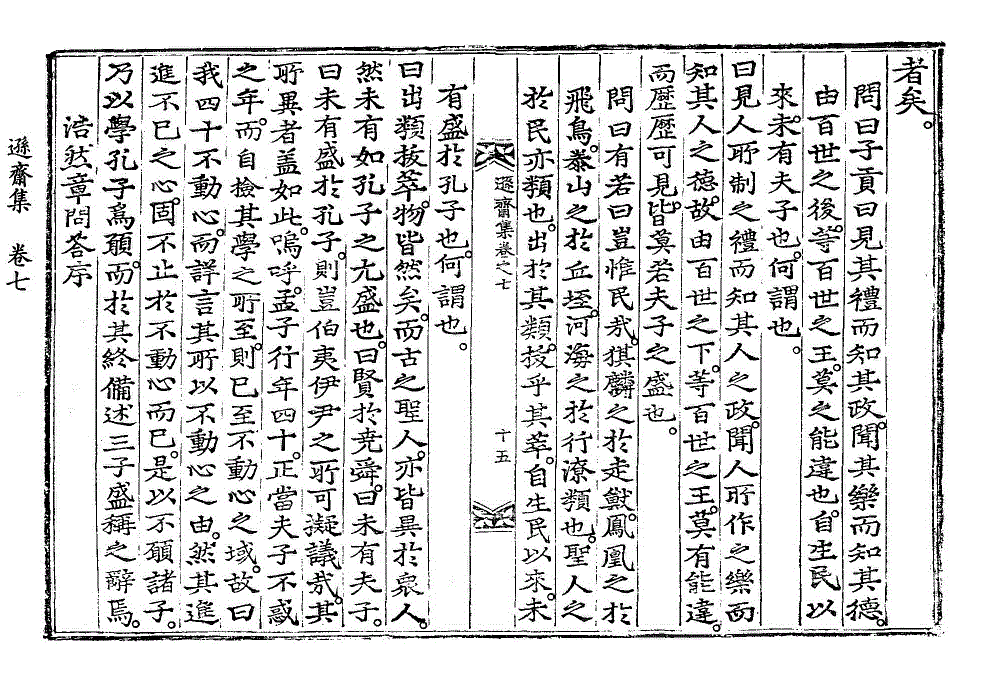 者矣。
者矣。问曰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何谓也。
曰见人所制之礼而知其人之政。闻人所作之乐而知其人之德。故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有能违。而历历可见。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问曰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何谓也。
曰出类拔萃。物皆然矣。而古之圣人。亦皆异于众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也。曰贤于尧舜。曰未有夫子。曰未有盛于孔子。则岂伯夷,伊尹之所可拟议哉。其所异者盖如此。呜呼。孟子行年四十。正当夫子不惑之年。而自检其学之所至。则已至不动心之域。故曰我四十不动心。而详言其所以不动心之由。然其进进不已之心。固不止于不动心而已。是以不愿诸子。乃以学孔子为愿。而于其终备述三子盛称之辞焉。
浩然章问答序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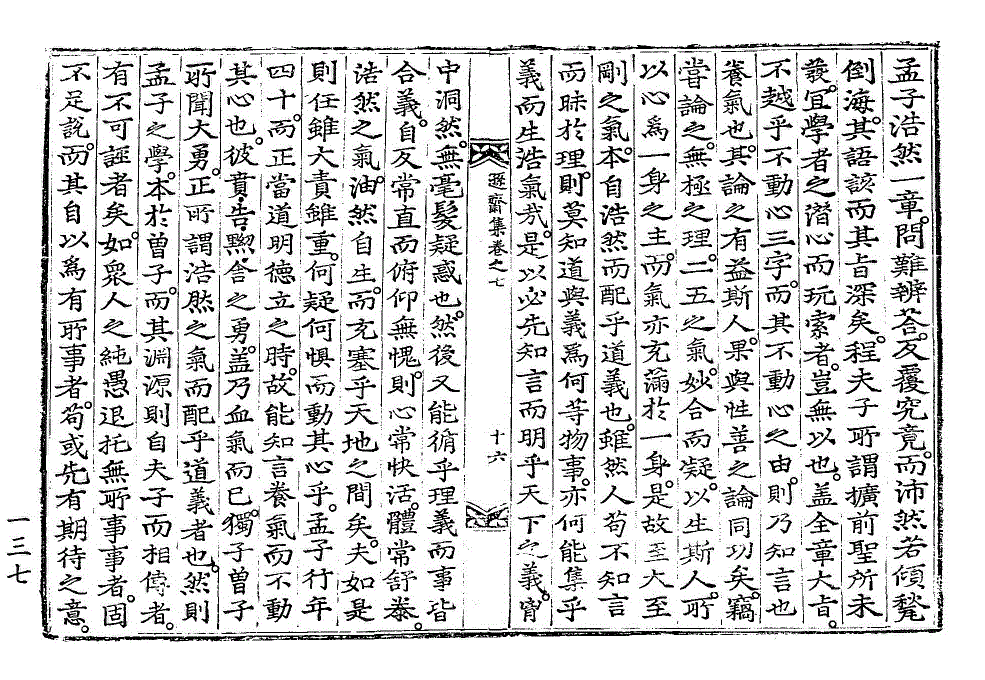 孟子浩然一章。问难辨答。反覆究竟。而沛然若倾甃倒海。其语该而其旨深矣。程夫子所谓扩前圣所未发。宜学者之潜心而玩索者。岂无以也。盖全章大旨。不越乎不动心三字。而其不动心之由。则乃知言也养气也。其论之有益斯人。果与性善之论同功矣。窃尝论之。无极之理。二五之气。妙合而凝。以生斯人。所以心为一身之主。而气亦充满于一身。是故至大至刚之气。本自浩然而配乎道义也。虽然人苟不知言而昧于理。则莫知道与义为何等物事。亦何能集乎义而生浩气哉。是以必先知言而明乎天下之义。胸中洞然。无毫发疑惑也。然后又能循乎理义而事皆合义。自反常直而俯仰无愧。则心常快活。体常舒泰。浩然之气。油然自生。而充塞乎天地之间矣。夫如是则任虽大责虽重。何疑何惧而动其心乎。孟子行年四十。而正当道明德立之时。故能知言养气而不动其心也。彼贲,告,黝,舍之勇。盖乃血气而已。独子曾子所闻大勇。正所谓浩然之气而配乎道义者也。然则孟子之学。本于曾子。而其渊源则自夫子而相传者。有不可诬者矣。如众人之纯愚退托无所事事者。固不足说。而其自以为有所事者。苟或先有期待之意。
孟子浩然一章。问难辨答。反覆究竟。而沛然若倾甃倒海。其语该而其旨深矣。程夫子所谓扩前圣所未发。宜学者之潜心而玩索者。岂无以也。盖全章大旨。不越乎不动心三字。而其不动心之由。则乃知言也养气也。其论之有益斯人。果与性善之论同功矣。窃尝论之。无极之理。二五之气。妙合而凝。以生斯人。所以心为一身之主。而气亦充满于一身。是故至大至刚之气。本自浩然而配乎道义也。虽然人苟不知言而昧于理。则莫知道与义为何等物事。亦何能集乎义而生浩气哉。是以必先知言而明乎天下之义。胸中洞然。无毫发疑惑也。然后又能循乎理义而事皆合义。自反常直而俯仰无愧。则心常快活。体常舒泰。浩然之气。油然自生。而充塞乎天地之间矣。夫如是则任虽大责虽重。何疑何惧而动其心乎。孟子行年四十。而正当道明德立之时。故能知言养气而不动其心也。彼贲,告,黝,舍之勇。盖乃血气而已。独子曾子所闻大勇。正所谓浩然之气而配乎道义者也。然则孟子之学。本于曾子。而其渊源则自夫子而相传者。有不可诬者矣。如众人之纯愚退托无所事事者。固不足说。而其自以为有所事者。苟或先有期待之意。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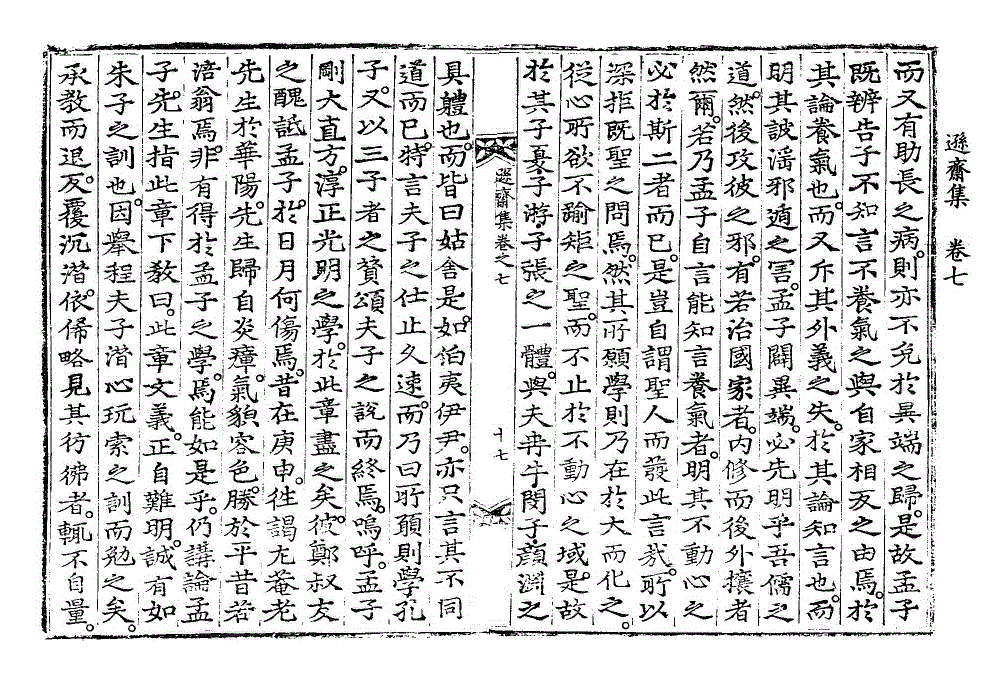 而又有助长之病。则亦不免于异端之归。是故孟子既辨告子不知言不养气之与自家相反之由焉。于其论养气也。而又斥其外义之失。于其论知言也。而明其诐淫邪遁之害。孟子辟异端。必先明乎吾儒之道。然后攻彼之邪。有若治国家者。内修而后外攘者然尔。若乃孟子自言能知言养气者。明其不动心之必于斯二者而已。是岂自谓圣人而发此言哉。所以深拒既圣之问焉。然其所愿学则乃在于大而化之。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圣。而不止于不动心之域。是故于其子夏,子游,子张之一体。与夫冉牛,闵子,颜渊之具体也。而皆曰姑舍是。如伯夷,伊尹。亦只言其不同道而已。特言夫子之仕止久速。而乃曰所愿则学孔子。又以三子者之赞颂夫子之说而终焉。呜呼。孟子刚大直方。淳正光明之学。于此章尽之矣。彼郑叔友之丑诋孟子。于日月何伤焉。昔在庚申。往谒尤庵老先生于华阳。先生归自炎瘴。气貌容色。胜于平昔若涪翁焉。非有得于孟子之学。焉能如是乎。仍讲论孟子。先生指此章下教曰。此章文义。正自难明。诚有如朱子之训也。因举程夫子潜心玩索之训而勉之矣。承教而退。反覆沉潜。依俙略见其彷佛者。辄不自量。
而又有助长之病。则亦不免于异端之归。是故孟子既辨告子不知言不养气之与自家相反之由焉。于其论养气也。而又斥其外义之失。于其论知言也。而明其诐淫邪遁之害。孟子辟异端。必先明乎吾儒之道。然后攻彼之邪。有若治国家者。内修而后外攘者然尔。若乃孟子自言能知言养气者。明其不动心之必于斯二者而已。是岂自谓圣人而发此言哉。所以深拒既圣之问焉。然其所愿学则乃在于大而化之。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圣。而不止于不动心之域。是故于其子夏,子游,子张之一体。与夫冉牛,闵子,颜渊之具体也。而皆曰姑舍是。如伯夷,伊尹。亦只言其不同道而已。特言夫子之仕止久速。而乃曰所愿则学孔子。又以三子者之赞颂夫子之说而终焉。呜呼。孟子刚大直方。淳正光明之学。于此章尽之矣。彼郑叔友之丑诋孟子。于日月何伤焉。昔在庚申。往谒尤庵老先生于华阳。先生归自炎瘴。气貌容色。胜于平昔若涪翁焉。非有得于孟子之学。焉能如是乎。仍讲论孟子。先生指此章下教曰。此章文义。正自难明。诚有如朱子之训也。因举程夫子潜心玩索之训而勉之矣。承教而退。反覆沉潜。依俙略见其彷佛者。辄不自量。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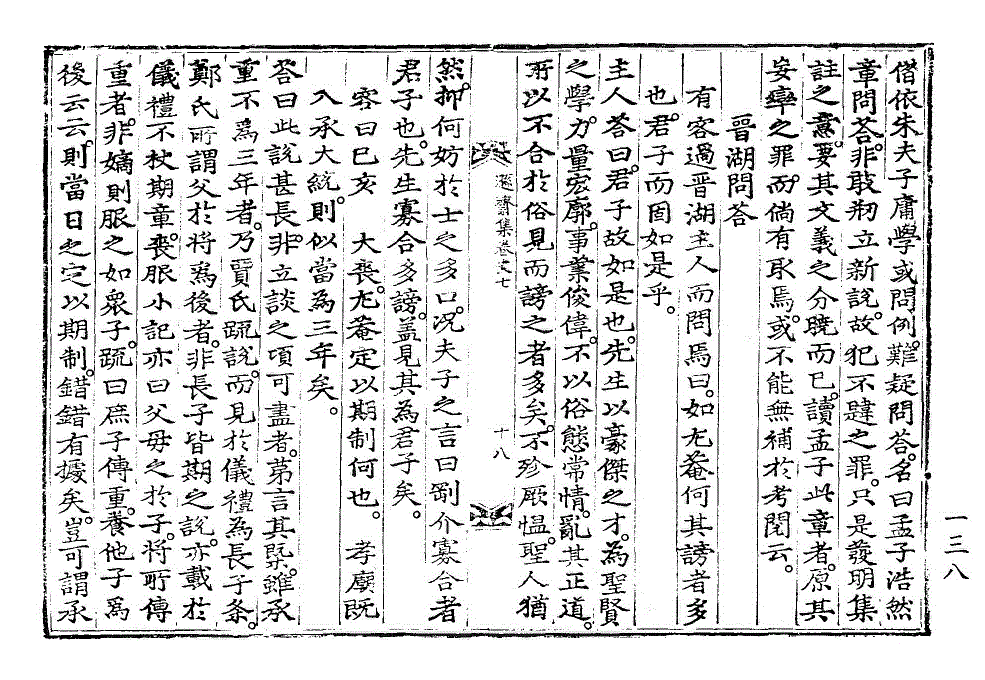 僭依朱夫子庸学或问例。难疑问答。名曰孟子浩然章问答。非敢刱立新说。故犯不韪之罪。只是发明集注之意。要其文义之分晓而已。读孟子此章者。原其妄率之罪。而倘有取焉。或不能无补于考阅云。
僭依朱夫子庸学或问例。难疑问答。名曰孟子浩然章问答。非敢刱立新说。故犯不韪之罪。只是发明集注之意。要其文义之分晓而已。读孟子此章者。原其妄率之罪。而倘有取焉。或不能无补于考阅云。晋湖问答
有客过晋湖主人而问焉曰。如尤庵何其谤者多也。君子而固如是乎。
主人答曰。君子故如是也。先生以豪杰之才。为圣贤之学。力量宏廓。事业俊伟。不以俗态常情。乱其正道。所以不合于俗见而谤之者多矣。不殄厥愠。圣人犹然。抑何妨于士之多口。况夫子之言曰刚介寡合者君子也。先生寡合多谤。盖见其为君子矣。
客曰己亥 大丧。尤庵定以期制何也。 孝庙既入承大统。则似当为三年矣。
答曰此说甚长。非立谈之顷可尽者。第言其槩。虽承重不为三年者。乃贾氏疏说。而见于仪礼为长子条。郑氏所谓父于将为后者。非长子皆期之说。亦载于仪礼不杖期章。丧服小记亦曰父母之于子。将所传重者。非嫡则服之如众子。疏曰庶子传重。养他子为后云云。则当日之定以期制。错错有据矣。岂可谓承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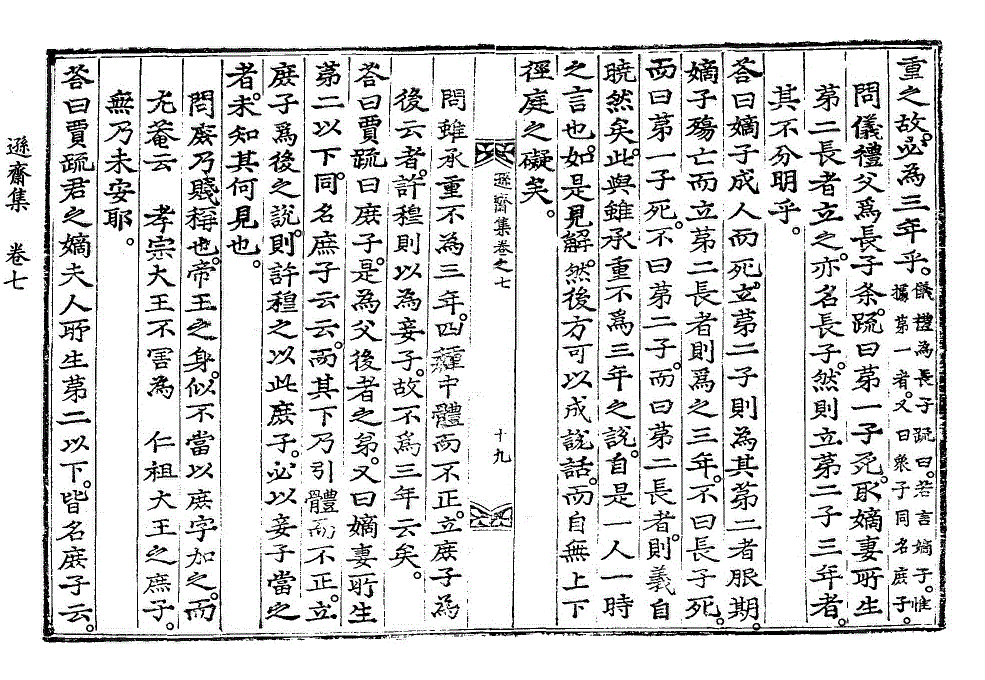 重之故。必为三年乎。(仪礼为长子疏曰。若言嫡子。惟据第一者。又曰众子同名庶子。)
重之故。必为三年乎。(仪礼为长子疏曰。若言嫡子。惟据第一者。又曰众子同名庶子。)问仪礼父为长子条。疏曰第一子死。取嫡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亦名长子。然则立第二子三年者。其不分明乎。
答曰嫡子成人而死。立第二子则为其第二者服期。嫡子殇亡而立第二长者则为之三年。不曰长子死。而曰第一子死。不曰第二子。而曰第二长者。则义自晓然矣。此与虽承重不为三年之说。自是一人一时之言也。如是见解。然后方可以成说话。而自无上下径庭之碍矣。
问虽承重不为三年。四种中体而不正。立庶子为后云者。许穆则以为妾子。故不为三年云矣。
答曰贾疏曰庶子。是为父后者之弟。又曰嫡妻所生第二以下。同名庶子云云。而其下乃引体而不正。立庶子为后之说。则许穆之以此庶子。必以妾子当之者。未知其何见也。
问庶乃贱称也。帝王之身。似不当以庶字加之。而尤庵云 孝宗大王不害为 仁祖大王之庶子。无乃未安耶。
答曰贾疏君之嫡夫人所生第二以下。皆名庶子云。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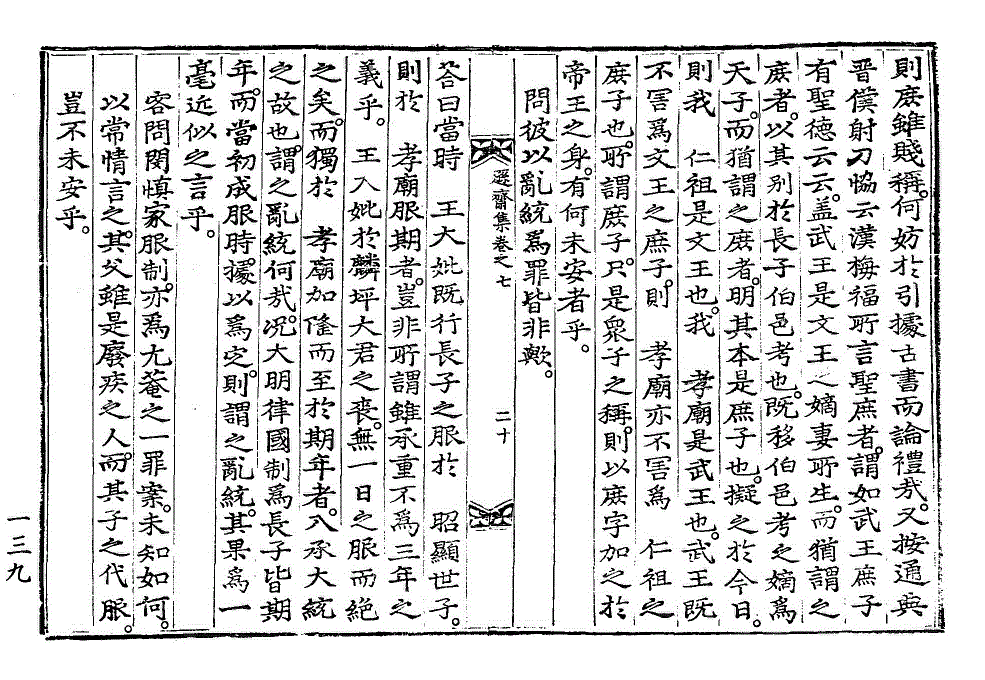 则庶虽贱称。何妨于引据古书而论礼哉。又按通典晋仆射刁协云汉梅福所言圣庶者。谓如武王庶子有圣德云云。盖武王是文王之嫡妻所生。而犹谓之庶者。以其别于长子伯邑考也。既移伯邑考之嫡为天子。而犹谓之庶者。明其本是庶子也。拟之于今日。则我 仁祖是文王也。我 孝庙是武王也。武王既不害为文王之庶子。则 孝庙亦不害为 仁祖之庶子也。所谓庶子。只是众子之称。则以庶字加之于帝王之身。有何未安者乎。
则庶虽贱称。何妨于引据古书而论礼哉。又按通典晋仆射刁协云汉梅福所言圣庶者。谓如武王庶子有圣德云云。盖武王是文王之嫡妻所生。而犹谓之庶者。以其别于长子伯邑考也。既移伯邑考之嫡为天子。而犹谓之庶者。明其本是庶子也。拟之于今日。则我 仁祖是文王也。我 孝庙是武王也。武王既不害为文王之庶子。则 孝庙亦不害为 仁祖之庶子也。所谓庶子。只是众子之称。则以庶字加之于帝王之身。有何未安者乎。问彼以乱统为罪皆非欤。
答曰当时 王大妣既行长子之服于 昭显世子。则于 孝庙服期者。岂非所谓虽承重不为三年之义乎。 王大妣于麟坪大君之丧。无一日之服而绝之矣。而独于 孝庙加隆而至于期年者。入承大统之故也。谓之乱统何哉。况大明律国制为长子皆期年。而当初成服时。据以为定。则谓之乱统。其果为一毫近似之言乎。
客问闵慎家服制。亦为尤庵之一罪案。未知如何。以常情言之。其父虽是废疾之人。而其子之代服。岂不未安乎。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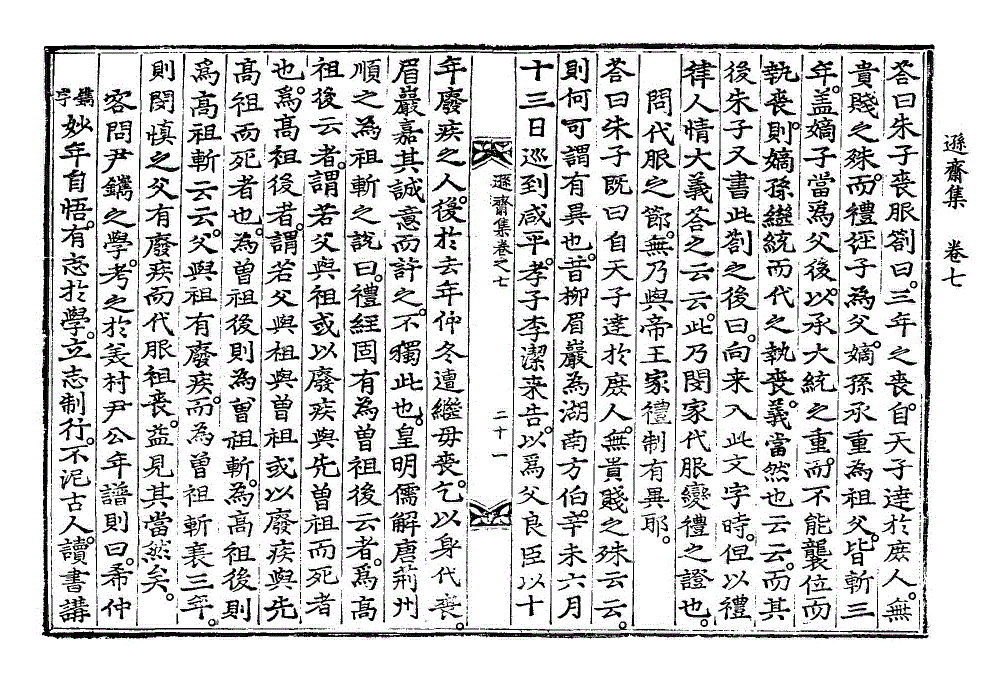 答曰朱子丧服劄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而礼经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三年。盖嫡子当为父后。以承大统之重。而不能袭位而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云云。而其后朱子又书此劄之后曰。向来入此文字时。但以礼律人情大义答之云云。此乃闵家代服变礼之證也。
答曰朱子丧服劄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而礼经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三年。盖嫡子当为父后。以承大统之重。而不能袭位而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云云。而其后朱子又书此劄之后曰。向来入此文字时。但以礼律人情大义答之云云。此乃闵家代服变礼之證也。问代服之节。无乃与帝王家礼制有异耶。
答曰朱子既曰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云云。则何可谓有异也。昔柳眉岩为湖南方伯。辛未六月十三日巡到咸平。孝子李洁来告。以为父良臣以十年废疾之人。复于去年仲冬遭继母丧。乞以身代丧。眉岩嘉其诚意而许之。不独此也。皇明儒解唐荆州顺之为祖斩之说曰。礼经固有为曾祖后云者。为高祖后云者。谓若父与祖或以废疾与先曾祖而死者也。为高祖后者。谓若父与祖与曾祖或以废疾与先高祖而死者也。为曾祖后则为曾祖斩。为高祖后则为高祖斩云云。父与祖有废疾。而为曾祖斩衰三年。则闵慎之父有废疾而代服祖丧。益见其当然矣。
客问尹镌(一作鑴)之学。考之于美村尹公年谱则曰。希仲 镌(一作鑴)字 妙年自悟。有志于学。立志制行。不泥古人。读书讲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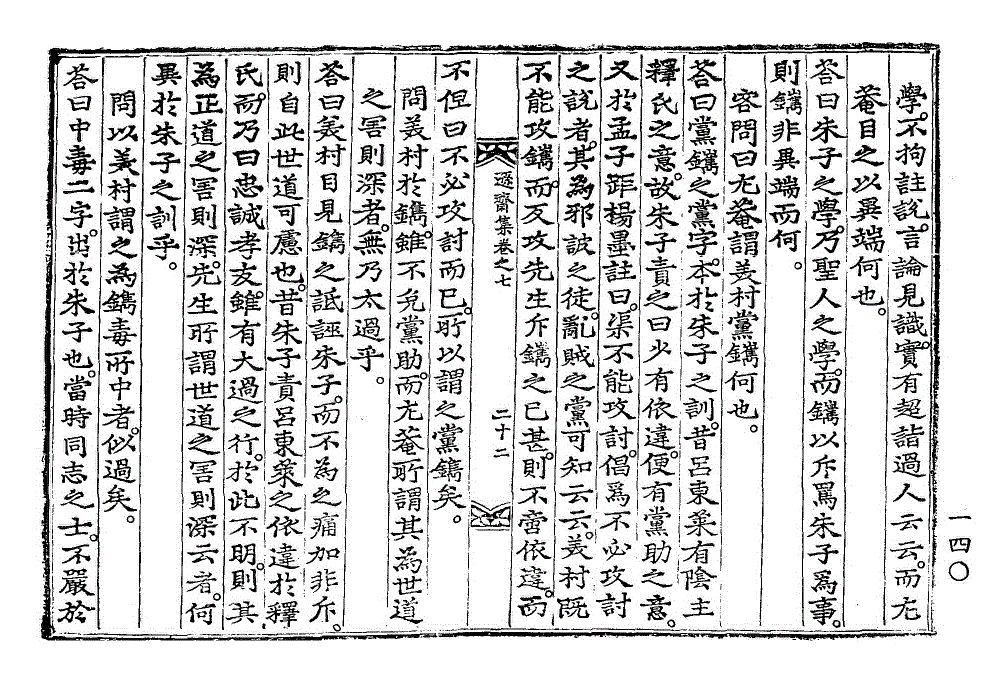 学。不拘注说。言论见识。实有超诣过人云云。而尤庵目之以异端何也。
学。不拘注说。言论见识。实有超诣过人云云。而尤庵目之以异端何也。答曰朱子之学。乃圣人之学。而镌(一作鑴)以斥骂朱子为事。则镌(一作鑴)非异端而何。
客问曰尤庵谓美村党镌(一作鑴)何也。
答曰党镌(一作鑴)之党字。本于朱子之训。昔吕东莱有阴主释氏之意。故朱子责之曰少有依违。便有党助之意。又于孟子距杨墨注曰。渠不能攻讨。倡为不必攻讨之说者。其为邪诐之徒。乱贼之党可知云云。美村既不能攻镌(一作鑴)。而反攻先生斥镌(一作鑴)之已甚。则不啻依违。而不但曰不必攻讨而已。所以谓之党镌(一作鑴)矣。
问美村于镌(一作鑴)。虽不免党助。而尤庵所谓其为世道之害则深者。无乃太过乎。
答曰美村目见镌(一作鑴)之诋诬朱子。而不为之痛加非斥。则自此世道可虑也。昔朱子责吕东莱之依违于释氏。而乃曰忠诚孝友。虽有大过之行。于此不明。则其为正道之害则深。先生所谓世道之害则深云者。何异于朱子之训乎。
问以美村谓之为镌(一作鑴)毒所中者。似过矣。
答曰中毒二字。出于朱子也。当时同志之士。不严于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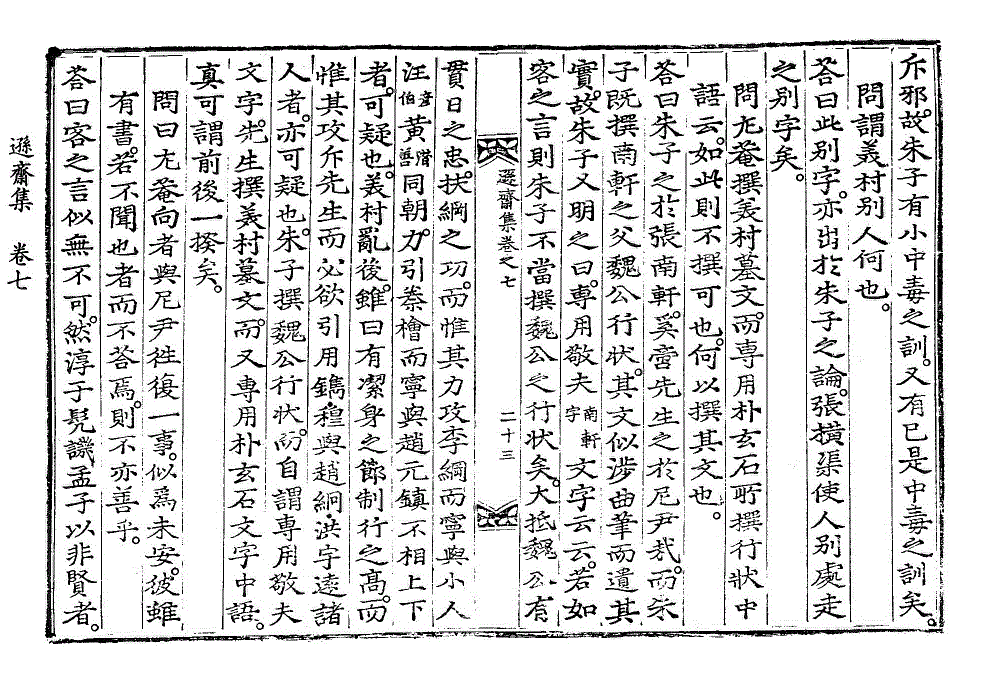 斥邪。故朱子有小中毒之训。又有已是中毒之训矣。
斥邪。故朱子有小中毒之训。又有已是中毒之训矣。问谓美村别人何也。
答曰此别字。亦出于朱子之论。张横渠使人别处走之别字矣。
问尤庵撰美村墓文。而专用朴玄石所撰行状中语云。如此则不撰可也。何以撰其文也。
答曰朱子之于张南轩。奚啻先生之于尼尹哉。而朱子既撰南轩之父魏公行状。其文似涉曲笔而遗其实。故朱子又明之曰。专用敬夫(南轩字)文字云云。若如客之言则朱子不当撰魏公之行状矣。大抵魏公有贯日之忠。扶纲之功。而惟其力攻李纲而宁与小人汪(彦伯)黄(潜善)同朝。力引秦桧而宁与赵元镇不相上下者。可疑也。美村乱后。虽曰有洁身之节制行之高。而惟其攻斥先生而必欲引用镌(一作鑴),穆与赵絅,洪宇远诸人者。亦可疑也。朱子撰魏公行状。而自谓专用敬夫文字。先生撰美村墓文。而又专用朴玄石文字中语。真可谓前后一揆矣。
问曰尤庵向者与尼尹往复一事。似为未安。彼虽有书。若不闻也者而不答焉。则不亦善乎。
答曰客之言似无不可。然淳于髡讥孟子以非贤者。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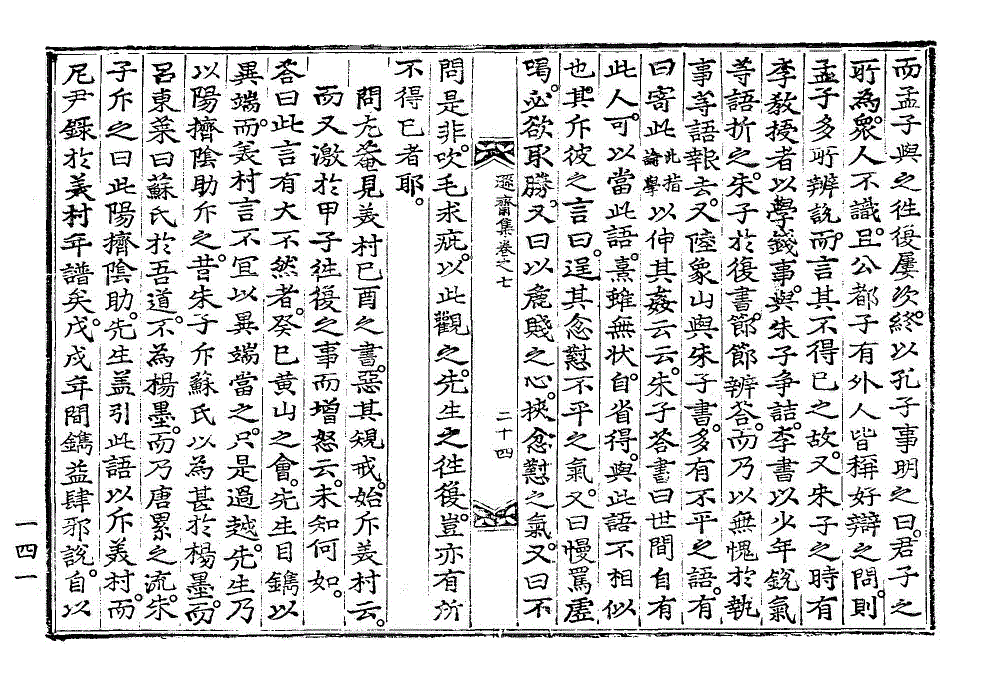 而孟子与之往复屡次。终以孔子事明之曰。君子之所为。众人不识。且公都子有外人皆称好辩之问。则孟子多所辨说。而言其不得已之故。又朱子之时有李教授者以学钱事。与朱子争诘。李书以少年锐气等语折之。朱子于复书。节节辨答。而乃以无愧于执事等语报去。又陆象山与朱子书。多有不平之语。有曰寄此(此指论学)以伸其奸云云。朱子答书曰世间自有此人。可以当此语。熹虽无状。自省得。与此语不相似也。其斥彼之言曰。逞其忿怼不平之气。又曰慢骂虚喝。必欲取胜。又曰以粗贱之心。挟忿怼之气。又曰不问是非。吹毛求疵。以此观之。先生之往复。岂亦有所不得已者耶。
而孟子与之往复屡次。终以孔子事明之曰。君子之所为。众人不识。且公都子有外人皆称好辩之问。则孟子多所辨说。而言其不得已之故。又朱子之时有李教授者以学钱事。与朱子争诘。李书以少年锐气等语折之。朱子于复书。节节辨答。而乃以无愧于执事等语报去。又陆象山与朱子书。多有不平之语。有曰寄此(此指论学)以伸其奸云云。朱子答书曰世间自有此人。可以当此语。熹虽无状。自省得。与此语不相似也。其斥彼之言曰。逞其忿怼不平之气。又曰慢骂虚喝。必欲取胜。又曰以粗贱之心。挟忿怼之气。又曰不问是非。吹毛求疵。以此观之。先生之往复。岂亦有所不得已者耶。问尤庵见美村己酉之书。恶其规戒。始斥美村云。而又激于甲子往复之事而增怒云。未知何如。
答曰此言有大不然者。癸巳黄山之会。先生目镌(一作鑴)以异端。而美村言不宜以异端当之。只是过越。先生乃以阳挤阴助斥之。昔朱子斥苏氏以为甚于杨墨。而吕东莱曰苏氏于吾道。不为杨墨。而乃唐累之流。朱子斥之曰此阳挤阴助。先生盖引此语以斥美村。而尼尹录于美村年谱矣。戊戌年间镌(一作鑴)益肆邪说。自以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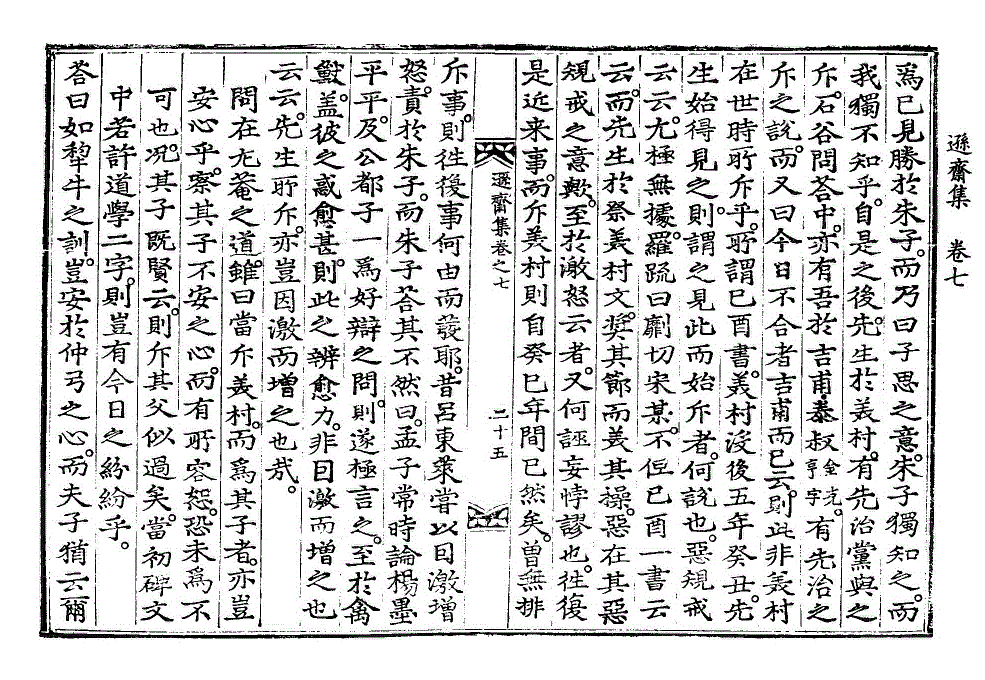 为已见胜于朱子。而乃曰子思之意。朱子独知之。而我独不知乎。自是之后。先生于美村。有先治党与之斥。石谷问答中。亦有吾于吉甫,泰叔(金克亨字。)有先治之斥之说。而又曰今日不合者吉甫而已云。则此非美村在世时所斥乎。所谓己酉书。美村没后五年癸丑。先生始得见之。则谓之见此而始斥者。何说也。恶规戒云云。尤极无据。罗疏曰劘切宋某。不但己酉一书云云。而先生于祭美村文。奖其节而美其操。恶在其恶规戒之意欤。至于激怒云者。又何诬妄悖谬也。往复是近来事。而斥美村则自癸巳年间已然矣。曾无排斥事。则往复事何由而发耶。昔吕东莱尝以因激增怒。责于朱子。而朱子答其不然曰。孟子常时论杨墨平平。及公都子一为好辩之问。则遂极言之。至于禽兽。盖彼之惑愈甚。则此之辨愈力。非因激而增之也云云。先生所斥。亦岂因激而增之也哉。
为已见胜于朱子。而乃曰子思之意。朱子独知之。而我独不知乎。自是之后。先生于美村。有先治党与之斥。石谷问答中。亦有吾于吉甫,泰叔(金克亨字。)有先治之斥之说。而又曰今日不合者吉甫而已云。则此非美村在世时所斥乎。所谓己酉书。美村没后五年癸丑。先生始得见之。则谓之见此而始斥者。何说也。恶规戒云云。尤极无据。罗疏曰劘切宋某。不但己酉一书云云。而先生于祭美村文。奖其节而美其操。恶在其恶规戒之意欤。至于激怒云者。又何诬妄悖谬也。往复是近来事。而斥美村则自癸巳年间已然矣。曾无排斥事。则往复事何由而发耶。昔吕东莱尝以因激增怒。责于朱子。而朱子答其不然曰。孟子常时论杨墨平平。及公都子一为好辩之问。则遂极言之。至于禽兽。盖彼之惑愈甚。则此之辨愈力。非因激而增之也云云。先生所斥。亦岂因激而增之也哉。问在尤庵之道。虽曰当斥美村。而为其子者。亦岂安心乎。察其子不安之心。而有所容恕。恐未为不可也。况其子既贤云。则斥其父似过矣。当初碑文中若许道学二字。则岂有今日之纷纷乎。
答曰如犁牛之训。岂安于仲弓之心。而夫子犹云尔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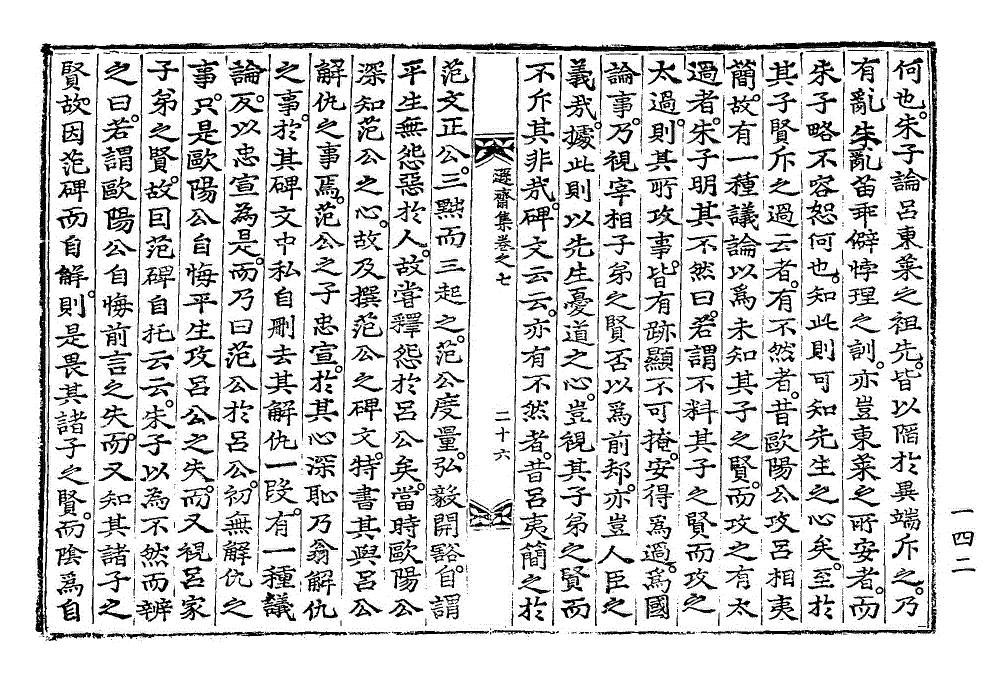 何也。朱子论吕东莱之祖先。皆以陷于异端斥之。乃有乱朱乱苗乖僻悖理之训。亦岂东莱之所安者。而朱子略不容恕何也。知此则可知先生之心矣。至于其子贤斥之过云者。有不然者。昔欧阳公攻吕相夷简。故有一种议论以为未知其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朱子明其不然曰。若谓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则其所攻。事皆有迹。显不可掩。安得为过。为国论事。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亦岂人臣之义哉。据此则以先生忧道之心。岂视其子弟之贤而不斥其非哉。碑文云云。亦有不然者。昔吕夷简之于范文正公。三黜而三起之。范公度量。弘毅开豁。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人。故尝释怨于吕公矣。当时欧阳公深知范公之心。故及撰范公之碑文。特书其与吕公解仇之事焉。范公之子忠宣。于其心深耻乃翁解仇之事。于其碑文中私自删去其解仇一段。有一种议论。反以忠宣为是。而乃曰范公于吕公。初无解仇之事。只是欧阳公自悔平生攻吕公之失。而又视吕家子弟之贤。故因范碑自托云云。朱子以为不然而辨之曰。若谓欧阳公自悔前言之失。而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而自解。则是畏其诸子之贤。而阴为自
何也。朱子论吕东莱之祖先。皆以陷于异端斥之。乃有乱朱乱苗乖僻悖理之训。亦岂东莱之所安者。而朱子略不容恕何也。知此则可知先生之心矣。至于其子贤斥之过云者。有不然者。昔欧阳公攻吕相夷简。故有一种议论以为未知其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朱子明其不然曰。若谓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则其所攻。事皆有迹。显不可掩。安得为过。为国论事。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亦岂人臣之义哉。据此则以先生忧道之心。岂视其子弟之贤而不斥其非哉。碑文云云。亦有不然者。昔吕夷简之于范文正公。三黜而三起之。范公度量。弘毅开豁。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人。故尝释怨于吕公矣。当时欧阳公深知范公之心。故及撰范公之碑文。特书其与吕公解仇之事焉。范公之子忠宣。于其心深耻乃翁解仇之事。于其碑文中私自删去其解仇一段。有一种议论。反以忠宣为是。而乃曰范公于吕公。初无解仇之事。只是欧阳公自悔平生攻吕公之失。而又视吕家子弟之贤。故因范碑自托云云。朱子以为不然而辨之曰。若谓欧阳公自悔前言之失。而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而自解。则是畏其诸子之贤。而阴为自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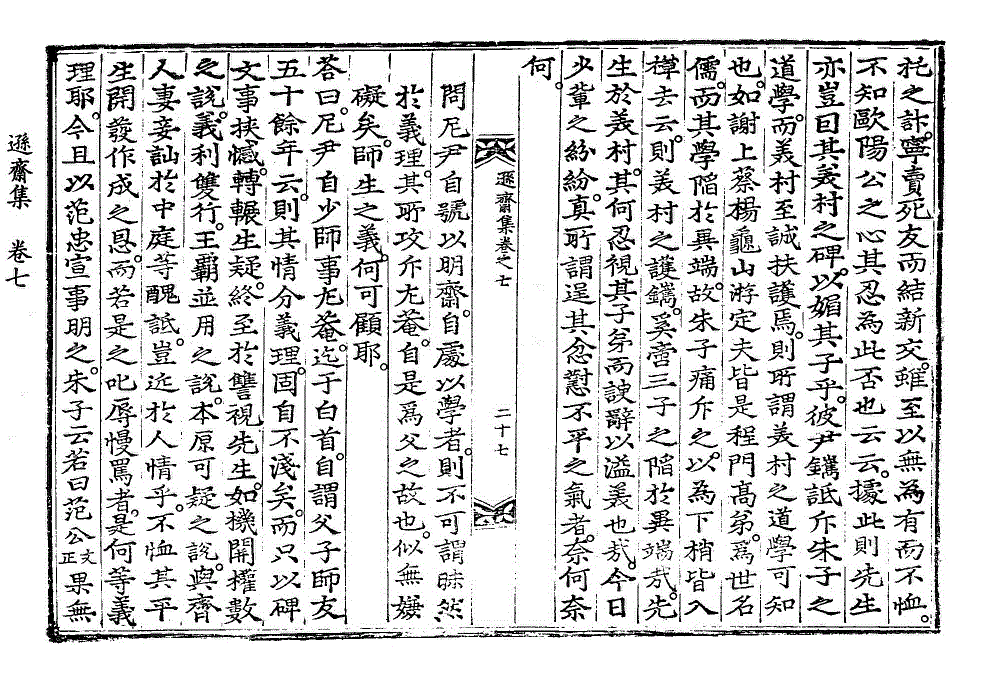 托之计。宁卖死友而结新交。虽至以无为有而不恤。不知欧阳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云云。据此则先生亦岂因其美村之碑。以媚其子乎。彼尹镌(一作鑴)诋斥朱子之道学。而美村至诚扶护焉。则所谓美村之道学可知也。如谢上蔡,杨龟山,游定夫皆是程门高弟。为世名儒。而其学陷于异端。故朱子痛斥之。以为下梢皆入禅去云。则美村之护镌(一作鑴)。奚啻三子之陷于异端哉。先生于美村。其何忍视其子弟而谀辞以溢美也哉。今日少辈之纷纷。真所谓逞其忿怼不平之气者。奈何奈何。
托之计。宁卖死友而结新交。虽至以无为有而不恤。不知欧阳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云云。据此则先生亦岂因其美村之碑。以媚其子乎。彼尹镌(一作鑴)诋斥朱子之道学。而美村至诚扶护焉。则所谓美村之道学可知也。如谢上蔡,杨龟山,游定夫皆是程门高弟。为世名儒。而其学陷于异端。故朱子痛斥之。以为下梢皆入禅去云。则美村之护镌(一作鑴)。奚啻三子之陷于异端哉。先生于美村。其何忍视其子弟而谀辞以溢美也哉。今日少辈之纷纷。真所谓逞其忿怼不平之气者。奈何奈何。问尼尹自号以明斋。自处以学者。则不可谓昧然于义理。其所攻斥尤庵。自是为父之故也。似无嫌碍矣。师生之义。何可顾耶。
答曰。尼尹自少师事尤庵。迄于白首。自谓父子师友五十馀年云。则其情分义理。固自不浅矣。而只以碑文事挟憾。转辗生疑。终至于雠视先生。如机关权数之说。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本原可疑之说。与齐人妻妾讪于中庭等丑诋。岂近于人情乎。不恤其平生开发作成之恩。而若是之叱辱慢骂者。是何等义理耶。今且以范忠宣事明之。朱子云若曰范公(文正)果无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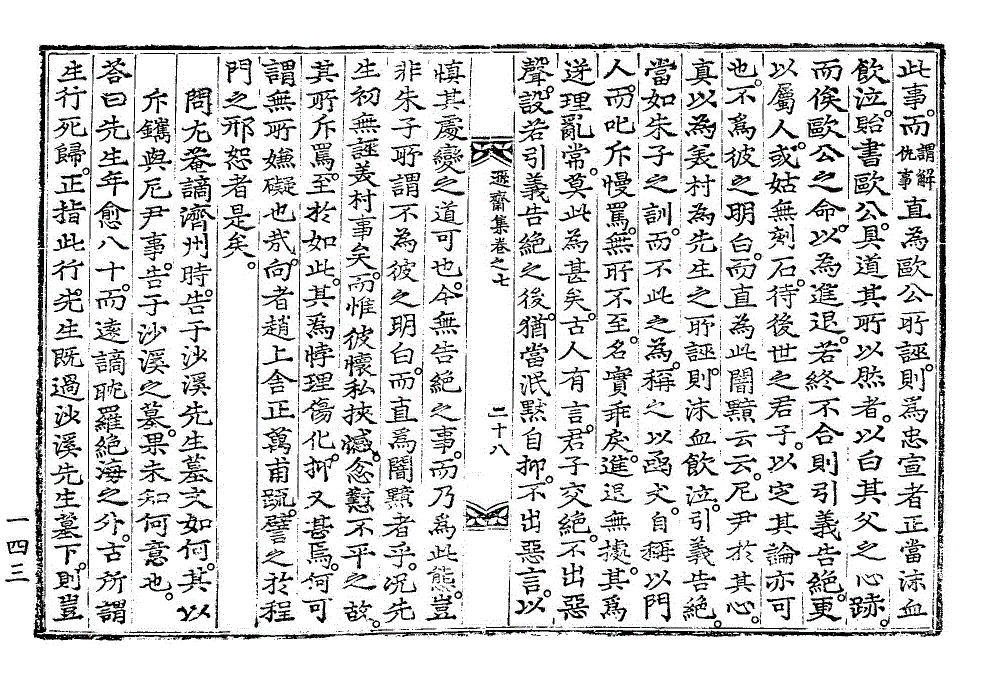 此事。而(谓解仇事)直为欧公所诬。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贻书欧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若终不合则引义告绝。更以属人。或姑无刻石。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亦可也。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闇黯云云。尼尹于其心。真以为美村为先生之所诬。则沫血饮泣。引义告绝。当如朱子之训。而不此之为。称之以函丈。自称以门人。而叱斥慢骂。无所不至。名实乖戾。进退无据。其为逆理乱常。莫此为甚矣。古人有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设若引义告绝之后。犹当泯默自抑。不出恶言。以慎其处变之道可也。今无告绝之事。而乃为此态。岂非朱子所谓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闇黯者乎。况先生初无诬美村事矣。而惟彼怀私挟憾。忿怼不平之故。其所斥骂。至于如此。其为悖理伤化。抑又甚焉。何可谓无所嫌碍也哉。向者赵上舍正万甫疏。譬之于程门之邢恕者是矣。
此事。而(谓解仇事)直为欧公所诬。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贻书欧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若终不合则引义告绝。更以属人。或姑无刻石。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亦可也。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闇黯云云。尼尹于其心。真以为美村为先生之所诬。则沫血饮泣。引义告绝。当如朱子之训。而不此之为。称之以函丈。自称以门人。而叱斥慢骂。无所不至。名实乖戾。进退无据。其为逆理乱常。莫此为甚矣。古人有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设若引义告绝之后。犹当泯默自抑。不出恶言。以慎其处变之道可也。今无告绝之事。而乃为此态。岂非朱子所谓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闇黯者乎。况先生初无诬美村事矣。而惟彼怀私挟憾。忿怼不平之故。其所斥骂。至于如此。其为悖理伤化。抑又甚焉。何可谓无所嫌碍也哉。向者赵上舍正万甫疏。譬之于程门之邢恕者是矣。问尤庵谪济州时。告于沙溪先生墓文如何。其以斥镌(一作鑴)与尼尹事。告于沙溪之墓。果未知何意也。
答曰先生年愈八十。而远谪耽罗绝海之外。古所谓生行死归。正指此行。先生既过沙溪先生墓下。则岂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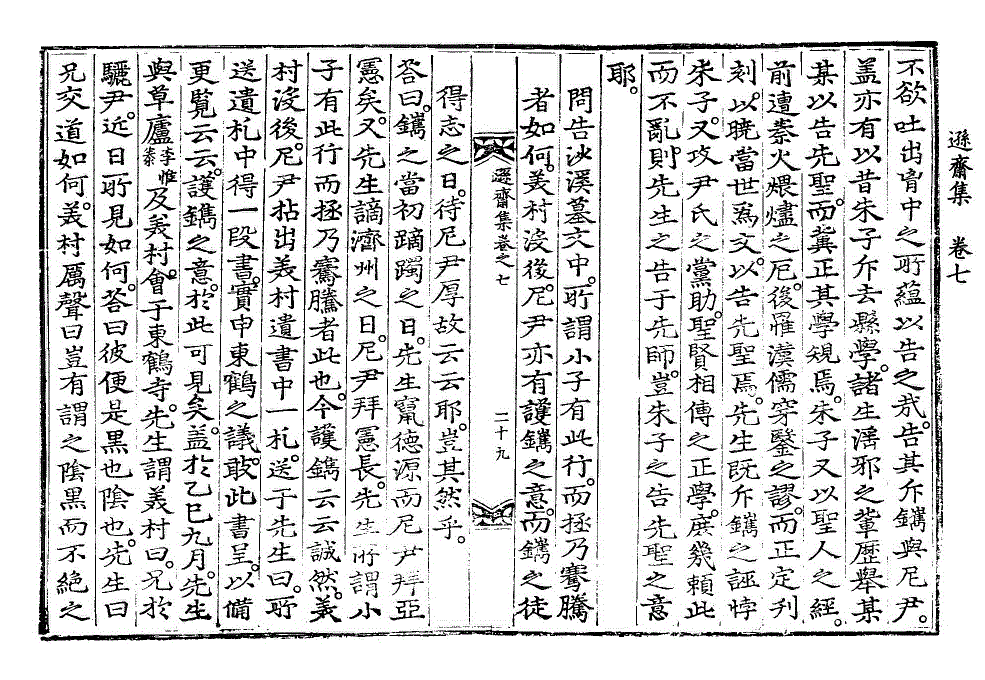 不欲吐出胸中之所蕴以告之哉。告其斥镌(一作鑴)与尼尹。盖亦有以昔朱子斥去县学。诸生淫邪之辈历举某某以告先圣。而冀正其学规焉。朱子又以圣人之经。前遭秦火煨烬之厄。后罹汉儒穿凿之谬。而正定刊刻。以晓当世为文。以告先圣焉。先生既斥镌(一作鑴)之诬悖朱子。又攻尹氏之党助。圣贤相传之正学。庶几赖此而不乱。则先生之告于先师。岂朱子之告先圣之意耶。
不欲吐出胸中之所蕴以告之哉。告其斥镌(一作鑴)与尼尹。盖亦有以昔朱子斥去县学。诸生淫邪之辈历举某某以告先圣。而冀正其学规焉。朱子又以圣人之经。前遭秦火煨烬之厄。后罹汉儒穿凿之谬。而正定刊刻。以晓当世为文。以告先圣焉。先生既斥镌(一作鑴)之诬悖朱子。又攻尹氏之党助。圣贤相传之正学。庶几赖此而不乱。则先生之告于先师。岂朱子之告先圣之意耶。问告沙溪墓文中。所谓小子有此行。而拯乃骞腾者如何。美村没后。尼尹亦有护镌(一作鑴)之意。而镌(一作鑴)之徒得志之日。待尼尹厚故云云耶。岂其然乎。
答曰。镌(一作鑴)之当初蹢躅之日。先生窜德源而尼尹拜亚宪矣。又先生谪济州之日。尼尹拜宪长。先生所谓小子有此行而拯乃骞腾者此也。今护镌(一作鑴)云云诚然。美村没后。尼尹拈出美村遗书中一札。送于先生曰。所送遗札中得一段书。实申东鹤之议。敢此书呈。以备更览云云。护镌(一作鑴)之意。于此可见矣。盖于乙巳九月。先生与草庐(李惟泰)及美村。会于东鹤寺。先生谓美村曰。兄于骊尹。近日所见如何。答曰彼便是黑也阴也。先生曰兄交道如何。美村厉声曰岂有谓之阴黑而不绝之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4L 页
 理乎。先生喜曰兄自此洒然矣。其后草庐谓先生曰吉甫外虽庄严。内实虚㥘。向者之言未可信也。先生曰岂有如许吉甫也。兄误矣。翌年三月美村抵书于先生曰。所谓阴黑之辩。只就其论议上而言。人品之鉴。又是别也。盖美村面从先生。而退有后言也。先生以书谢草庐曰。有知无知。奚止较三十里也。尼尹之所拈出一书。实申东鹤之议云者。乃美村三月书也。然则尼尹之意。岂不欲遵守美村右镌(一作鑴)之见。而以为定论也耶。先生在长鬐棘中时。尼尹往候矣。先生与李平康(芝村)书曰子仁来与相守云云。而言其恕镌(一作鑴)之事曰。恐为他日异论之种子云云。先生于当时。已知其他日必为异论。而明有恐击之事也。大抵尼尹之忿怼怨憾。实本于镌(一作鑴)事。而后来之攻斥先生。甚于镌(一作鑴)辈。则镌(一作鑴)之徒得志之日。宜乎先生之有此行。而尼尹之骞腾也。
理乎。先生喜曰兄自此洒然矣。其后草庐谓先生曰吉甫外虽庄严。内实虚㥘。向者之言未可信也。先生曰岂有如许吉甫也。兄误矣。翌年三月美村抵书于先生曰。所谓阴黑之辩。只就其论议上而言。人品之鉴。又是别也。盖美村面从先生。而退有后言也。先生以书谢草庐曰。有知无知。奚止较三十里也。尼尹之所拈出一书。实申东鹤之议云者。乃美村三月书也。然则尼尹之意。岂不欲遵守美村右镌(一作鑴)之见。而以为定论也耶。先生在长鬐棘中时。尼尹往候矣。先生与李平康(芝村)书曰子仁来与相守云云。而言其恕镌(一作鑴)之事曰。恐为他日异论之种子云云。先生于当时。已知其他日必为异论。而明有恐击之事也。大抵尼尹之忿怼怨憾。实本于镌(一作鑴)事。而后来之攻斥先生。甚于镌(一作鑴)辈。则镌(一作鑴)之徒得志之日。宜乎先生之有此行。而尼尹之骞腾也。客曰主人之开示甚详。而区区之见。犹不能无惑焉。今又推原其始而辨之可乎。镌(一作鑴)既自谓为学而多所辨释。如中庸文字辈。虽异于朱子注说。而乃以发明经旨为事。则尤庵之斥以邪说而谓之害将滔天者。无乃太刻乎。如美村之恕镌(一作鑴)而护之者。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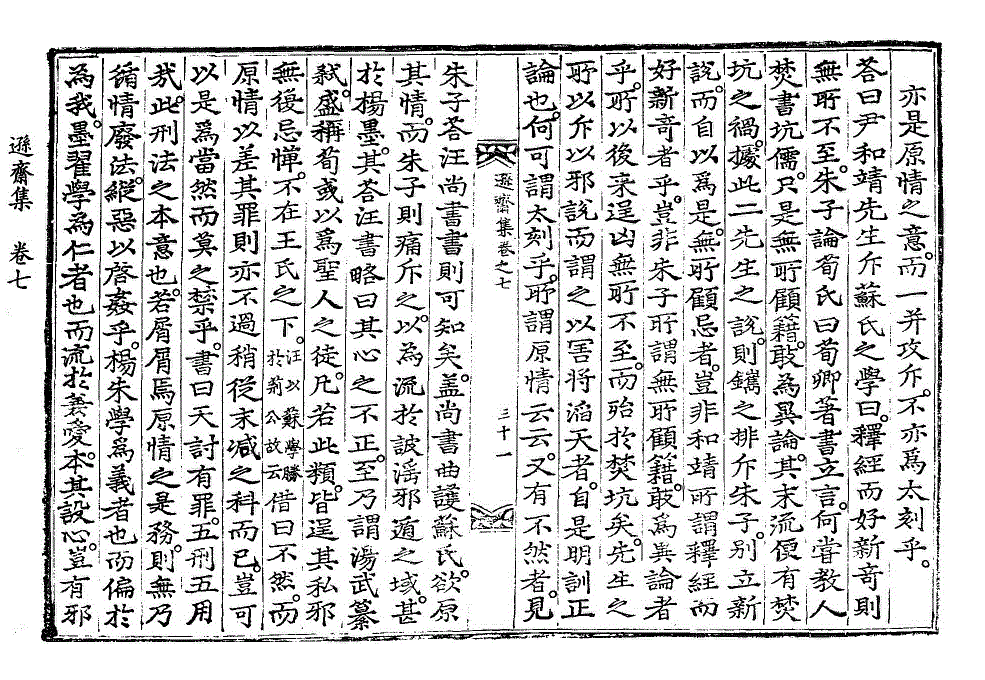 亦是原情之意。而一并攻斥。不亦为太刻乎。
亦是原情之意。而一并攻斥。不亦为太刻乎。答曰尹和靖先生斥苏氏之学曰。释经而好新奇则无所不至。朱子论荀氏曰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无所顾籍(一作藉)。敢为异论。其末流便有焚坑之祸。据此二先生之说。则镌(一作鑴)之排斥朱子。别立新说。而自以为是。无所顾忌者。岂非和靖所谓释经而好新奇者乎。岂非朱子所谓无所顾籍(一作藉)。敢为异论者乎。所以后来逞凶无所不至。而殆于焚坑矣。先生之所以斥以邪说而谓之以害将滔天者。自是明训正论也。何可谓太刻乎。所谓原情云云。又有不然者。见朱子答汪尚书书则可知矣。盖尚书曲护苏氏。欲原其情。而朱子则痛斥之。以为流于诐淫邪遁之域。甚于杨墨。其答汪书略曰其心之不正。至乃谓汤武纂弑。盛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凡若此类。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不在王氏之下。(汪以苏学胜于荆公故云)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则亦不过稍从末减之科而已。岂可以是为当然而莫之禁乎。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屑屑焉原情之是务。则无乃循情废法。纵恶以启奸乎。杨朱学为义者也而偏于为我。墨翟学为仁者也而流于兼爱。本其设心。岂有邪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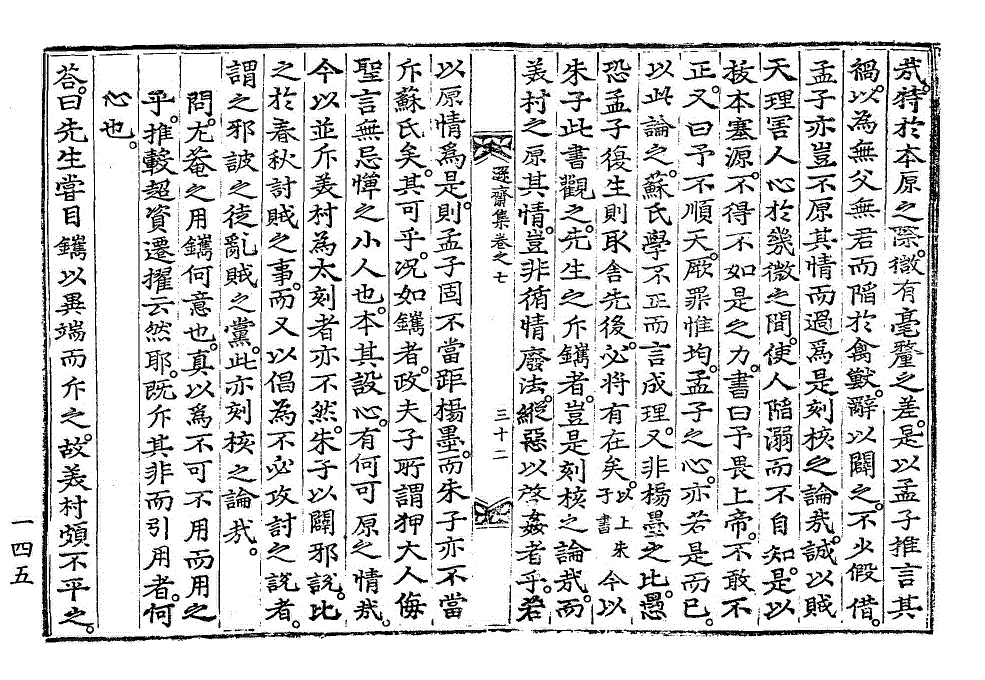 哉。特于本原之际。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祸。以为无父无君而陷于禽兽。辞以辟之。不少假借。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诚以贼天理害人心于几微之间。使人陷溺而不自知。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不顺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以此论之。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愚恐孟子复生则取舍先后。必将有在矣。(以上朱子书)今以朱子此书观之。先生之斥镌(一作鑴)者。岂是刻核之论哉。而美村之原其情。岂非循情废法。纵恶以启奸者乎。若以原情为是。则孟子固不当距杨墨。而朱子亦不当斥苏氏矣。其可乎。况如镌(一作鑴)者。政夫子所谓狎大人侮圣言无忌惮之小人也。本其设心。有何可原之情哉。今以并斥美村为太刻者亦不然。朱子以辟邪说。比之于春秋讨贼之事。而又以倡为不必攻讨之说者。谓之邪诐之徒乱贼之党。此亦刻核之论哉。
哉。特于本原之际。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祸。以为无父无君而陷于禽兽。辞以辟之。不少假借。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诚以贼天理害人心于几微之间。使人陷溺而不自知。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不顺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以此论之。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愚恐孟子复生则取舍先后。必将有在矣。(以上朱子书)今以朱子此书观之。先生之斥镌(一作鑴)者。岂是刻核之论哉。而美村之原其情。岂非循情废法。纵恶以启奸者乎。若以原情为是。则孟子固不当距杨墨。而朱子亦不当斥苏氏矣。其可乎。况如镌(一作鑴)者。政夫子所谓狎大人侮圣言无忌惮之小人也。本其设心。有何可原之情哉。今以并斥美村为太刻者亦不然。朱子以辟邪说。比之于春秋讨贼之事。而又以倡为不必攻讨之说者。谓之邪诐之徒乱贼之党。此亦刻核之论哉。问。尤庵之用镌(一作鑴)何意也。真以为不可不用而用之乎。推毂超资迁擢云然耶。既斥其非而引用者。何心也。
答曰。先生尝目镌(一作鑴)以异端而斥之。故美村颇不平之。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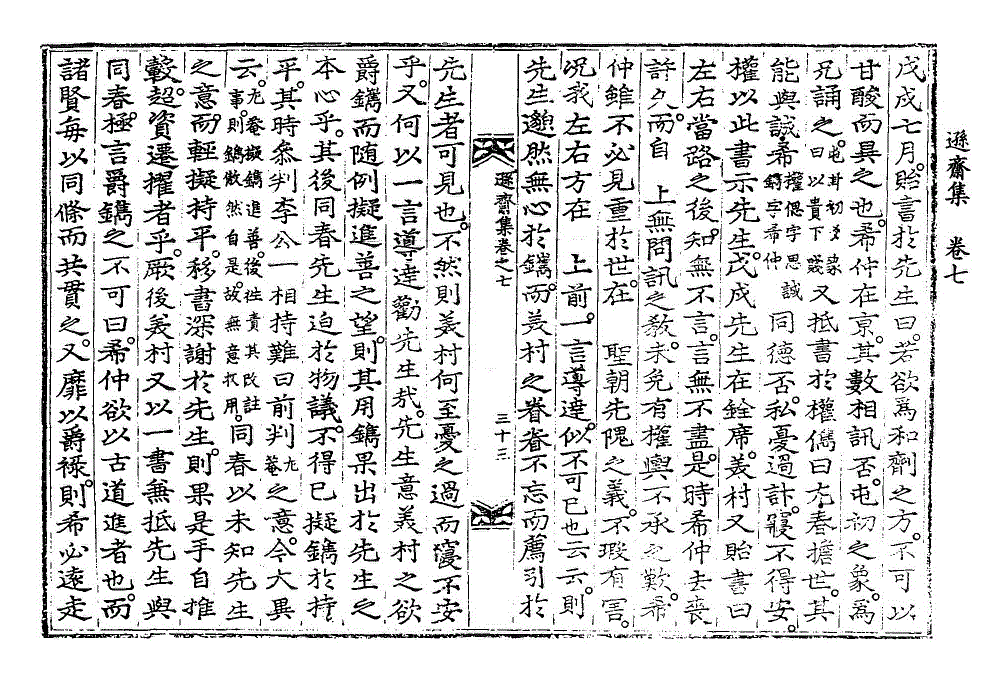 戊戌七月。贻书于先生曰。若欲为和剂之方。不可以甘酸而异之也。希仲在京。其数相讯否。屯初之象。为兄诵之。(屯卦初爻象曰以贵下贱)又抵书于权俊曰尤,春担世。其能与诚,希 权偲字思诚镌(一作鑴)字希仲 同德否。私忧过计。寝不得安。权以此书示先生。戊戌先生在铨席。美村又贻书曰左右当路之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时希仲去丧许久。而自 上无问讯之教。未免有权舆不承之叹。希仲虽不必见重于世。在 圣朝先隗之义。不瑕有害。况我左右方在 上前。一言导达。似不可已也云云。则先生邈然无心于镌(一作鑴)。而美村之眷眷不忘而荐引于先生者可见也。不然则美村何至忧之过而寝不安乎。又何以一言导达劝先生哉。先生意美村之欲爵镌(一作鑴)而随例拟进善之望。则其用镌(一作鑴)果出于先生之本心乎。其后同春先生迫于物议。不得已拟镌(一作鑴)于持平。其时参判李公一相持难曰前判(尤庵)之意。今大异云。尤庵拟镌(一作鑴)进善。后往责其改注事。则镌(一作鑴)傲然自是。故无意收用。 同春以未知先生之意。而轻拟持平。移书深谢于先生。则果是手自推毂。超资迁擢者乎。厥后美村又以一书兼抵先生与同春。极言爵镌(一作鑴)之不可曰。希仲欲以古道进者也。而诸贤每以同条而共贯之。又靡以爵禄。则希必远走
戊戌七月。贻书于先生曰。若欲为和剂之方。不可以甘酸而异之也。希仲在京。其数相讯否。屯初之象。为兄诵之。(屯卦初爻象曰以贵下贱)又抵书于权俊曰尤,春担世。其能与诚,希 权偲字思诚镌(一作鑴)字希仲 同德否。私忧过计。寝不得安。权以此书示先生。戊戌先生在铨席。美村又贻书曰左右当路之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时希仲去丧许久。而自 上无问讯之教。未免有权舆不承之叹。希仲虽不必见重于世。在 圣朝先隗之义。不瑕有害。况我左右方在 上前。一言导达。似不可已也云云。则先生邈然无心于镌(一作鑴)。而美村之眷眷不忘而荐引于先生者可见也。不然则美村何至忧之过而寝不安乎。又何以一言导达劝先生哉。先生意美村之欲爵镌(一作鑴)而随例拟进善之望。则其用镌(一作鑴)果出于先生之本心乎。其后同春先生迫于物议。不得已拟镌(一作鑴)于持平。其时参判李公一相持难曰前判(尤庵)之意。今大异云。尤庵拟镌(一作鑴)进善。后往责其改注事。则镌(一作鑴)傲然自是。故无意收用。 同春以未知先生之意。而轻拟持平。移书深谢于先生。则果是手自推毂。超资迁擢者乎。厥后美村又以一书兼抵先生与同春。极言爵镌(一作鑴)之不可曰。希仲欲以古道进者也。而诸贤每以同条而共贯之。又靡以爵禄。则希必远走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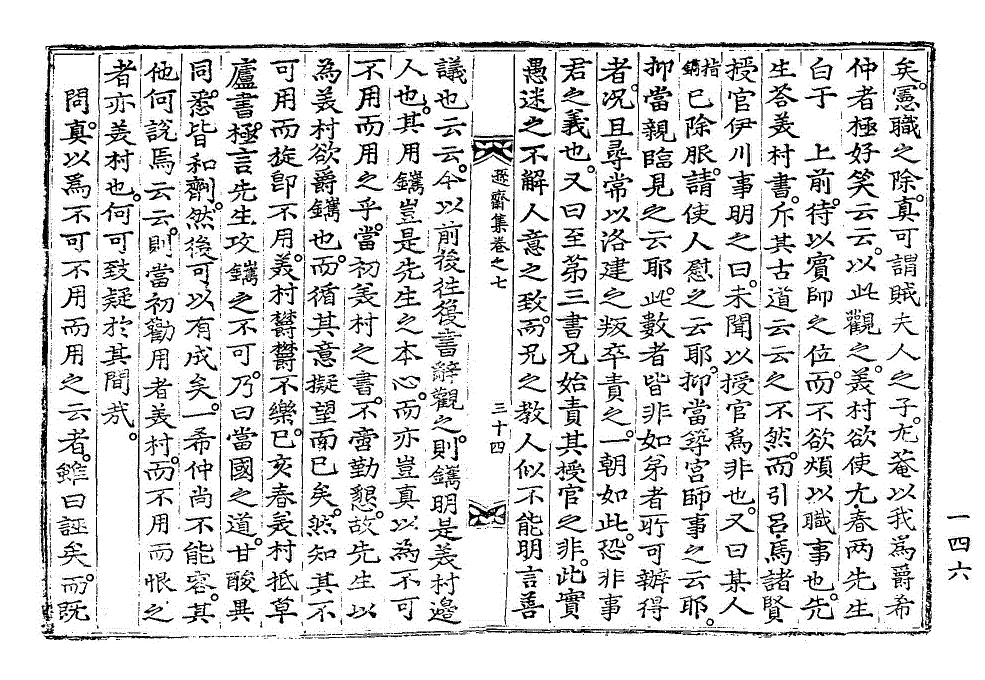 矣。宪职之除。真可谓贼夫人之子。尤庵以我为爵希仲者极好笑云云。以此观之。美村欲使尤,春两先生白于 上前。待以宾师之位。而不欲烦以职事也。先生答美村书。斥其古道云云之不然。而引吕,马诸贤授官伊川事明之曰。未闻以授官为非也。又曰某人 指镌(一作鑴) 已除服。请使人慰之云耶。抑当筑宫师事之云耶。抑当亲临见之云耶。此数者皆非如弟者所可办得者。况且寻常以洛建之叛卒责之。一朝如此。恐非事君之义也。又曰至第三书兄始责其授官之非。此实愚迷之不解人意之致。而兄之教人似不能明言善议也云云。今以前后往复书辞观之。则镌(一作鑴)明是美村边人也。其用镌(一作鑴)岂是先生之本心。而亦岂真以为不可不用而用之乎。当初美村之书。不啻勤恳。故先生以为美村欲爵镌(一作鑴)也。而循其意拟望而已矣。然知其不可用而旋即不用。美村郁郁不乐。己亥春美村抵草庐书。极言先生攻镌(一作鑴)之不可。乃曰当国之道。甘酸异同。悉皆和剂。然后可以有成矣。一希仲尚不能容。其他何说焉云云。则当初劝用者美村。而不用而恨之者亦美村也。何可致疑于其间哉。
矣。宪职之除。真可谓贼夫人之子。尤庵以我为爵希仲者极好笑云云。以此观之。美村欲使尤,春两先生白于 上前。待以宾师之位。而不欲烦以职事也。先生答美村书。斥其古道云云之不然。而引吕,马诸贤授官伊川事明之曰。未闻以授官为非也。又曰某人 指镌(一作鑴) 已除服。请使人慰之云耶。抑当筑宫师事之云耶。抑当亲临见之云耶。此数者皆非如弟者所可办得者。况且寻常以洛建之叛卒责之。一朝如此。恐非事君之义也。又曰至第三书兄始责其授官之非。此实愚迷之不解人意之致。而兄之教人似不能明言善议也云云。今以前后往复书辞观之。则镌(一作鑴)明是美村边人也。其用镌(一作鑴)岂是先生之本心。而亦岂真以为不可不用而用之乎。当初美村之书。不啻勤恳。故先生以为美村欲爵镌(一作鑴)也。而循其意拟望而已矣。然知其不可用而旋即不用。美村郁郁不乐。己亥春美村抵草庐书。极言先生攻镌(一作鑴)之不可。乃曰当国之道。甘酸异同。悉皆和剂。然后可以有成矣。一希仲尚不能容。其他何说焉云云。则当初劝用者美村。而不用而恨之者亦美村也。何可致疑于其间哉。问。真以为不可不用而用之云者。虽曰诬矣。而既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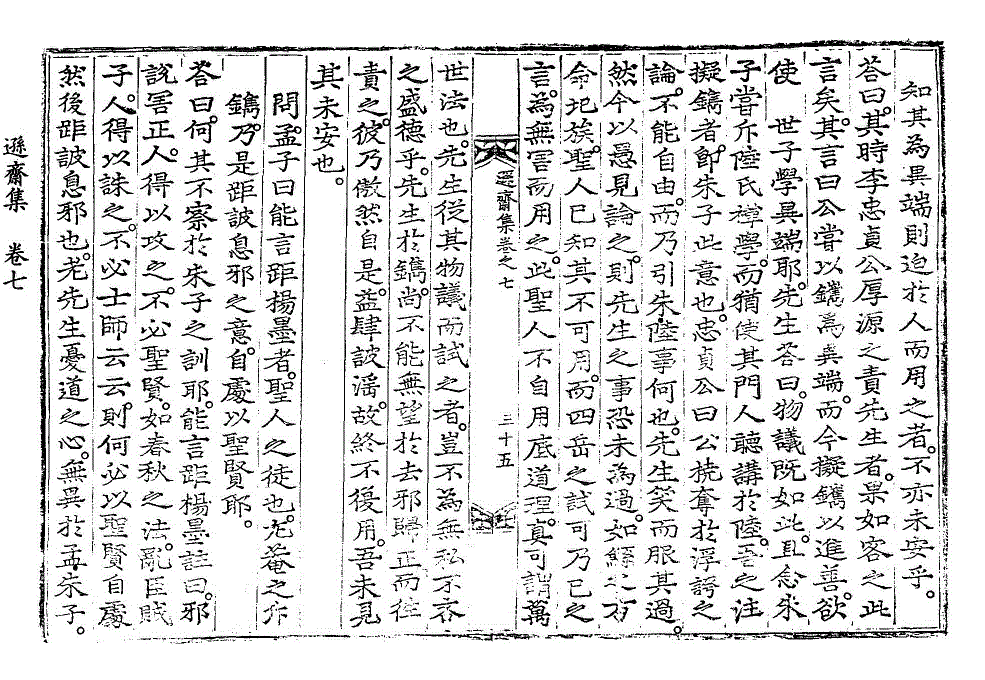 知其为异端则迫于人而用之者。不亦未安乎。
知其为异端则迫于人而用之者。不亦未安乎。答曰。其时李忠贞公厚源之责先生者。果如客之此言矣。其言曰公尝以镌(一作鑴)为异端。而今拟镌(一作鑴)以进善。欲使 世子学异端耶。先生答曰。物议既如此。且念朱子尝斥陆氏禅学。而犹使其门人听讲于陆。吾之注拟镌(一作鑴)者。即朱子此意也。忠贞公曰公挠夺于浮誇之论。不能自由。而乃引朱,陆事何也。先生笑而服其过。然今以愚见论之。则先生之事恐未为过。如鲧之方命圮族。圣人已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之试可乃已之言。为无害而用之。此圣人不自用底道理。真可谓万世法也。先生从其物议而试之者。岂不为无私不吝之盛德乎。先生于镌(一作鑴)。尚不能无望于去邪归正而往责之。彼乃傲然自是。益肆诐淫。故终不复用。吾未见其未安也。
问。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尤庵之斥镌(一作鑴)。乃是距诐息邪之意。自处以圣贤耶。
答曰。何其不察于朱子之训耶。能言距杨墨注曰。邪说害正。人得以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得以诛之。不必士师云云。则何必以圣贤自处然后距诐息邪也。老先生忧道之心。无异于孟,朱子。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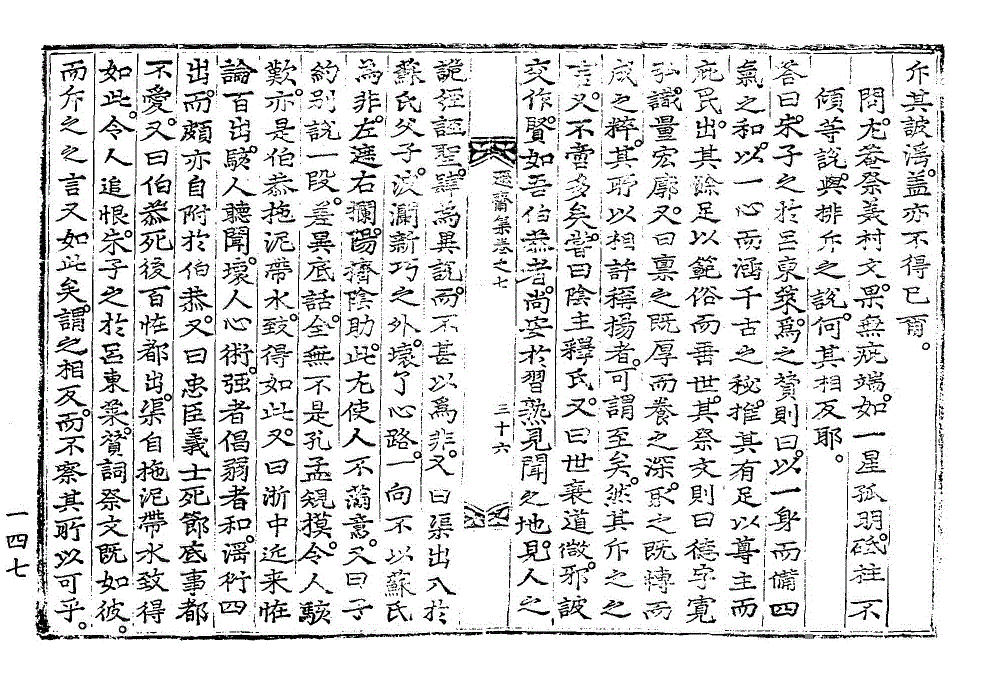 斥其诐淫。盖亦不得已尔。
斥其诐淫。盖亦不得已尔。问。尤庵祭美村文。果无疵端。如一星孤明。砥柱不倾等说。与排斥之说。何其相反耶。
答曰。朱子之于吕东莱。为之赞则曰。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馀足以范俗而垂世。其祭文则曰德字宽弘。识量宏廓。又曰禀之既厚而养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其所以相许称扬者。可谓至矣。然其斥之之言。又不啻多矣。尝曰阴主释氏。又曰世衰道微。邪诐交作。贤如吾伯恭者。尚安于习熟见闻之地。见人之诡经诬圣。肆为异说。而不甚以为非。又曰渠出入于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坏了心路。一向不以苏氏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又曰子约别说一段。差异底话。全无不是孔孟规摸。令人骇叹。亦是伯恭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曰浙中近来怪论百出。骇人听闻。坏人心术。强者倡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颇亦自附于伯恭。又曰忠臣义士死节底事都不爱。又曰伯恭死后百怪都出。渠自拖泥带水致得如此。令人追恨。朱子之于吕东莱。赞词祭文既如彼。而斥之之言又如此矣。谓之相反。而不察其所以可乎。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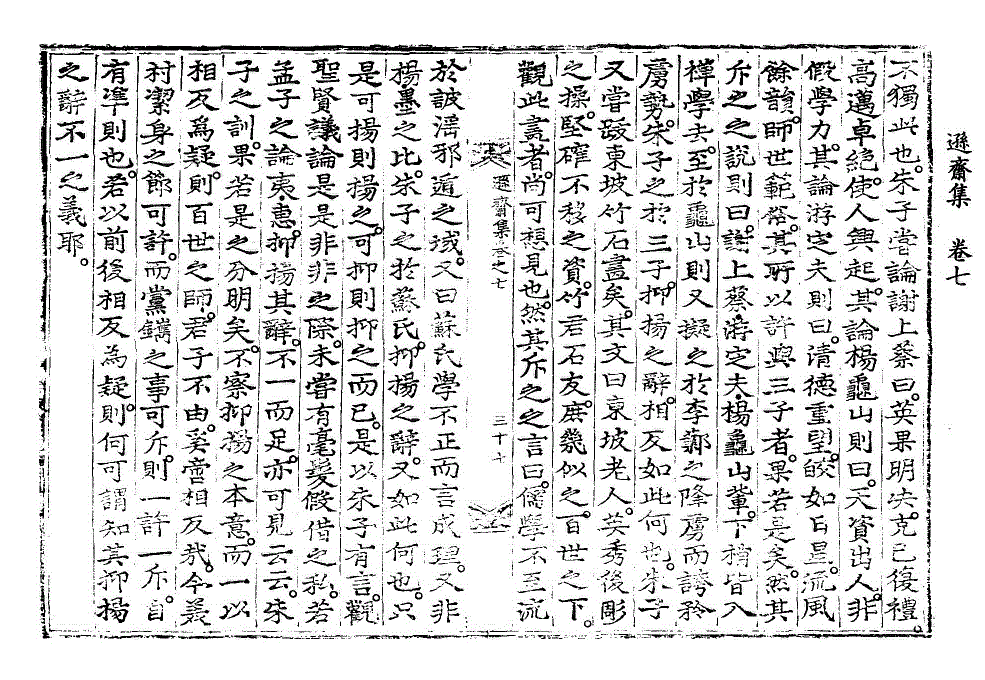 不独此也。朱子尝论谢上蔡曰。英果明决。克己复礼。高迈卓绝。使人兴起。其论杨龟山则曰。天资出人。非假学力。其论游定夫则曰。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风馀韵。师世范俗。其所以许与三子者。果若是矣。然其斥之之说则曰。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至于龟山则又拟之于李邺之降虏而誇矜虏势。朱子之于三子。抑扬之辞。相反如此何也。朱子又尝跋东坡竹石画矣。其文曰东坡老人。英秀后彫之操。坚确不移之资。竹君石友。庶几似之。百世之下。观此画者。尚可想见也。然其斥之之言曰。儒学不至流于诐淫邪遁之域。又曰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朱子之于苏氏。抑扬之辞。又如此何也。只是可扬则扬之。可抑则抑之而已。是以朱子有言。观圣贤议论是是非非之际。未尝有毫发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论夷,惠。抑扬其辞。不一而足。亦可见云云。朱子之训。果若是之分明矣。不察抑扬之本意。而一以相反为疑。则百世之师。君子不由。奚啻相反哉。今美村洁身之节可许。而党镌(一作鑴)之事可斥。则一许一斥。自有准则也。若以前后相反为疑。则何可谓知其抑扬之辞不一之义耶。
不独此也。朱子尝论谢上蔡曰。英果明决。克己复礼。高迈卓绝。使人兴起。其论杨龟山则曰。天资出人。非假学力。其论游定夫则曰。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风馀韵。师世范俗。其所以许与三子者。果若是矣。然其斥之之说则曰。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至于龟山则又拟之于李邺之降虏而誇矜虏势。朱子之于三子。抑扬之辞。相反如此何也。朱子又尝跋东坡竹石画矣。其文曰东坡老人。英秀后彫之操。坚确不移之资。竹君石友。庶几似之。百世之下。观此画者。尚可想见也。然其斥之之言曰。儒学不至流于诐淫邪遁之域。又曰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朱子之于苏氏。抑扬之辞。又如此何也。只是可扬则扬之。可抑则抑之而已。是以朱子有言。观圣贤议论是是非非之际。未尝有毫发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论夷,惠。抑扬其辞。不一而足。亦可见云云。朱子之训。果若是之分明矣。不察抑扬之本意。而一以相反为疑。则百世之师。君子不由。奚啻相反哉。今美村洁身之节可许。而党镌(一作鑴)之事可斥。则一许一斥。自有准则也。若以前后相反为疑。则何可谓知其抑扬之辞不一之义耶。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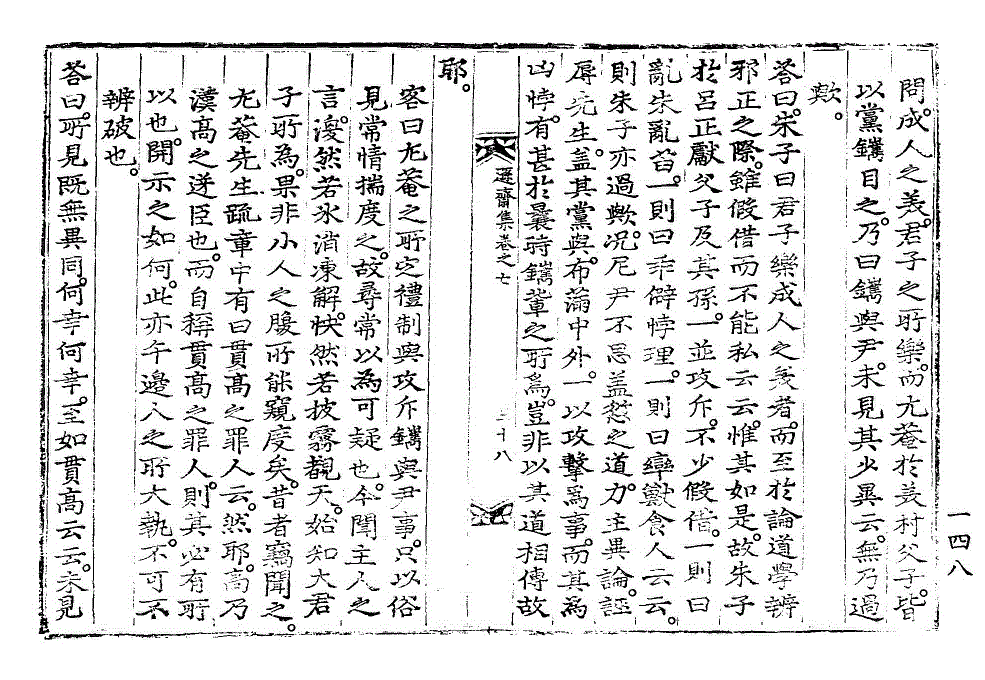 问。成人之美。君子之所乐。而尤庵于美村父子。皆以党镌(一作鑴)目之。乃曰镌(一作鑴)与尹。未见其少异云。无乃过欤。
问。成人之美。君子之所乐。而尤庵于美村父子。皆以党镌(一作鑴)目之。乃曰镌(一作鑴)与尹。未见其少异云。无乃过欤。答曰。朱子曰君子乐成人之美者。而至于论道学辨邪正之际。虽假借而不能私云云。惟其如是。故朱子于吕正献父子及其孙。一并攻斥。不少假借。一则曰乱朱乱苗。一则曰乖僻悖理。一则曰率兽食人云云。则朱子亦过欤。况尼尹不思盖愆之道。力主异论。诬辱先生。盖其党与。布满中外。一以攻击为事。而其为凶悖。有甚于曩时镌(一作鑴)辈之所为。岂非以其道相传故耶。
客曰尤庵之所定礼制与攻斥镌(一作鑴)与尹事。只以俗见常情揣度之。故寻常以为可疑也。今闻主人之言。涣然若冰消冻解。快然若披雾睹天。始知大君子所为。果非小人之腹所能窥度矣。昔者窃闻之。尤庵先生疏章中有曰贯高之罪人云。然耶。高乃汉高之逆臣也。而自称贯高之罪人。则其必有所以也。开示之如何。此亦午边人之所大执。不可不辨破也。
答曰。所见既无异同。何幸何幸。至如贯高云云。未见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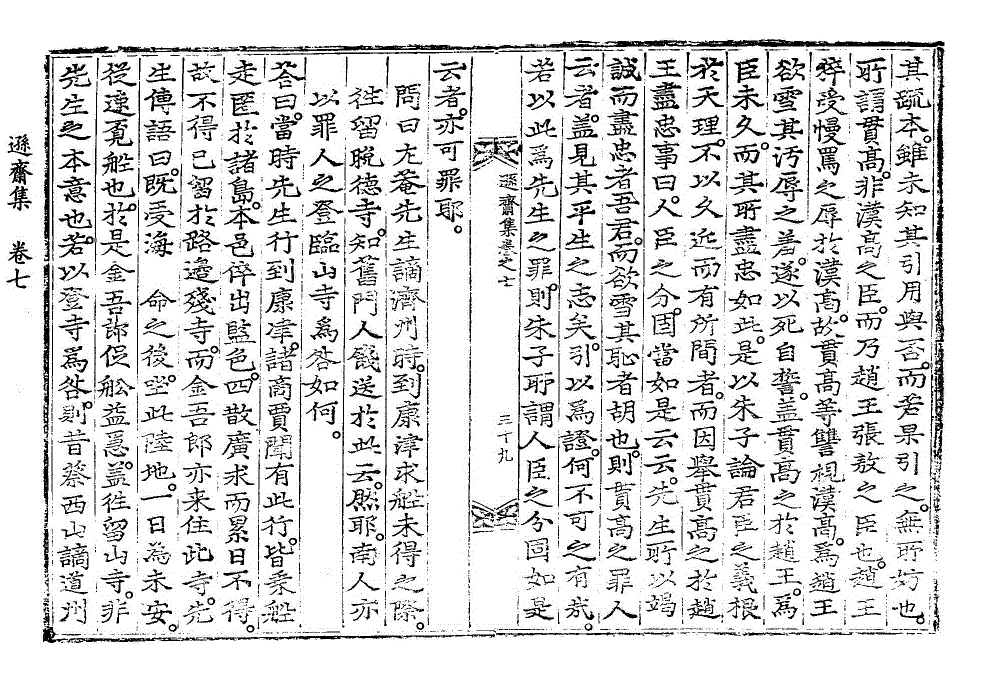 其疏本。虽未知其引用与否。而若果引之。无所妨也。所谓贯高。非汉高之臣。而乃赵王张敖之臣也。赵王猝受慢骂之辱于汉高。故贯高等雠视汉高。为赵王欲雪其污辱之羞。遂以死自誓。盖贯高之于赵王。为臣未久。而其所尽忠如此。是以朱子论君臣之义根于天理。不以久近而有所间者。而因举贯高之于赵王尽忠事曰。人臣之分。固当如是云云。先生所以竭诚而尽忠者吾君。而欲雪其耻者胡也。则贯高之罪人云者。盖见其平生之志矣。引以为證。何不可之有哉。若以此为先生之罪。则朱子所谓人臣之分固如是云者。亦可罪耶。
其疏本。虽未知其引用与否。而若果引之。无所妨也。所谓贯高。非汉高之臣。而乃赵王张敖之臣也。赵王猝受慢骂之辱于汉高。故贯高等雠视汉高。为赵王欲雪其污辱之羞。遂以死自誓。盖贯高之于赵王。为臣未久。而其所尽忠如此。是以朱子论君臣之义根于天理。不以久近而有所间者。而因举贯高之于赵王尽忠事曰。人臣之分。固当如是云云。先生所以竭诚而尽忠者吾君。而欲雪其耻者胡也。则贯高之罪人云者。盖见其平生之志矣。引以为證。何不可之有哉。若以此为先生之罪。则朱子所谓人臣之分固如是云者。亦可罪耶。问曰尤庵先生谪济州时。到康津求船未得之际。往留晚德寺。知旧门人饯送于此云。然耶。南人亦以罪人之登临山寺为咎如何。
答曰。当时先生行到康津。诸商贾闻有此行。皆乘船走匿于诸岛。本邑倅出监色。四散广求而累日不得。故不得已留于路边残寺。而金吾郎亦来住此寺。先生传语曰。既受海 命之后。坐此陆地。一日为未安。从速觅船也。于是金吾郎促船益急。盖往留山寺。非先生之本意也。若以登寺为咎。则昔蔡西山谪道州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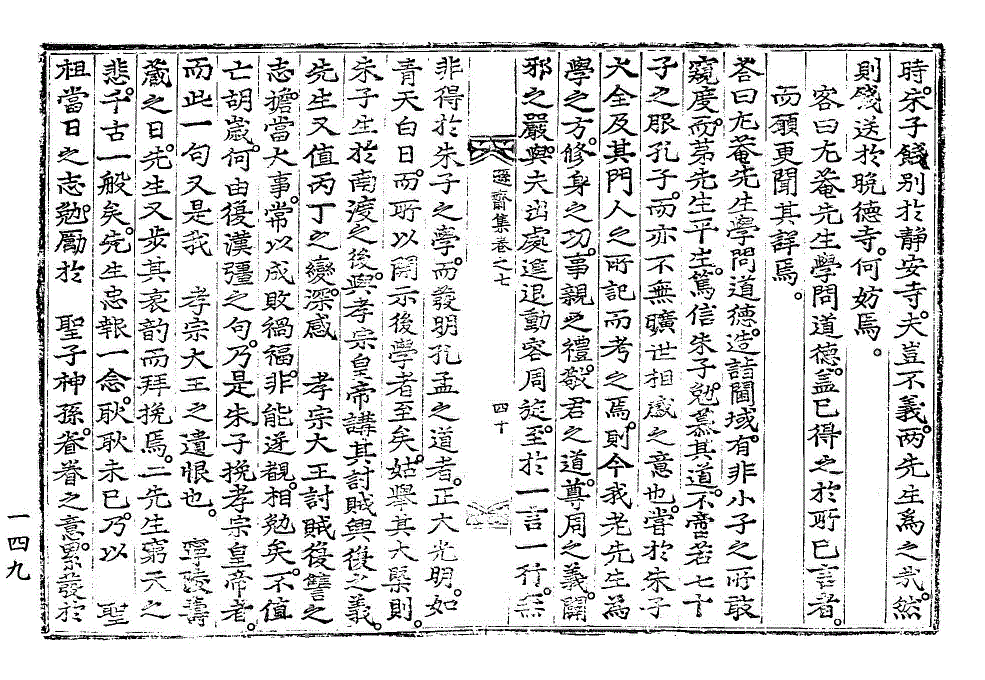 时。朱子饯别于静安寺。夫岂不义。两先生为之哉。然则饯送于晚德寺。何妨焉。
时。朱子饯别于静安寺。夫岂不义。两先生为之哉。然则饯送于晚德寺。何妨焉。客曰尤庵先生学问道德。盖已得之于所已言者。而愿更闻其详焉。
答曰尤庵先生学问道德。造诣阃域。有非小子之所敢窥度。而第先生平生。笃信朱子。勉慕其道。不啻若七十子之服孔子。而亦不无旷世相感之意也。尝于朱子大全及其门人之所记而考之焉。则今我老先生为学之方。修身之功。事亲之礼。敬君之道。尊周之义。辟邪之严。与夫出处进退动容周旋。至于一言一行。无非得于朱子之学。而发明孔孟之道者。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而所以开示后学者至矣。姑举其大槩则。朱子生于南渡之后。与孝宗皇帝讲其讨贼兴复之义。先生又值丙丁之变。深感 孝宗大王讨贼复雠之志。担当大事。常以成败祸福。非能逆睹。相勉矣。不值亡胡岁。何由复汉彊之句。乃是朱子挽孝宗皇帝者。而此一句又是我 孝宗大王之遗恨也。 宁陵寿藏之日。先生又步其哀韵而拜挽焉。二先生穷天之悲。千古一般矣。先生忠报一念。耿耿未已。乃以 圣祖当日之志。勉励于 圣子神孙。眷眷之意。累发于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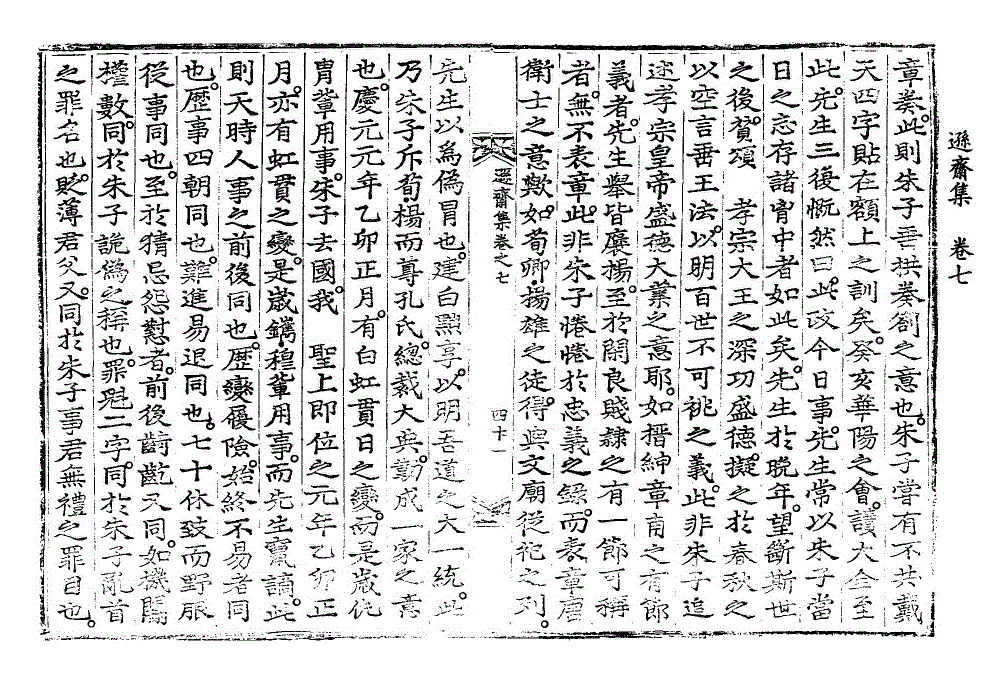 章奏。此则朱子垂拱奏劄之意也。朱子尝有不共戴天四字贴在额上之训矣。癸亥华阳之会。读大全至此。先生三复慨然曰。此政今日事。先生常以朱子当日之志存诸胸中者如此矣。先生于晚年。望断斯世之后。赞颂 孝宗大王之深功盛德。拟之于春秋之以空言垂王法。以明百世不可祧之义。此非朱子追述孝宗皇帝盛德大业之意耶。如搢绅章甫之有节义者。先生举皆褒扬。至于闲良贱隶之有一节可称者。无不表章。此非朱子惓惓于忠义之录。而表章唐卫士之意欤。如荀卿,扬雄之徒。得与文庙从祀之列。先生以为伪冒也。建白黜享。以明吾道之大一统。此乃朱子斥荀,杨(一作扬)而尊孔氏。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意也。庆元元年乙卯正月。有白虹贯日之变。而是岁仇胄辈用事。朱子去国。我 圣上即位之元年乙卯正月。亦有虹贯之变。是岁镌(一作鑴),穆辈用事。而先生窜谪。此则天时人事之前后同也。历变履险。始终不易者同也。历事四朝同也。难进易退同也。七十休致而野服从事同也。至于猜忌怨怼者。前后齮龁又同。如机关权数。同于朱子诡伪之称也。罪魁二字。同于朱子乱首之罪名也。贬薄君父。又同于朱子事君无礼之罪目也。
章奏。此则朱子垂拱奏劄之意也。朱子尝有不共戴天四字贴在额上之训矣。癸亥华阳之会。读大全至此。先生三复慨然曰。此政今日事。先生常以朱子当日之志存诸胸中者如此矣。先生于晚年。望断斯世之后。赞颂 孝宗大王之深功盛德。拟之于春秋之以空言垂王法。以明百世不可祧之义。此非朱子追述孝宗皇帝盛德大业之意耶。如搢绅章甫之有节义者。先生举皆褒扬。至于闲良贱隶之有一节可称者。无不表章。此非朱子惓惓于忠义之录。而表章唐卫士之意欤。如荀卿,扬雄之徒。得与文庙从祀之列。先生以为伪冒也。建白黜享。以明吾道之大一统。此乃朱子斥荀,杨(一作扬)而尊孔氏。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意也。庆元元年乙卯正月。有白虹贯日之变。而是岁仇胄辈用事。朱子去国。我 圣上即位之元年乙卯正月。亦有虹贯之变。是岁镌(一作鑴),穆辈用事。而先生窜谪。此则天时人事之前后同也。历变履险。始终不易者同也。历事四朝同也。难进易退同也。七十休致而野服从事同也。至于猜忌怨怼者。前后齮龁又同。如机关权数。同于朱子诡伪之称也。罪魁二字。同于朱子乱首之罪名也。贬薄君父。又同于朱子事君无礼之罪目也。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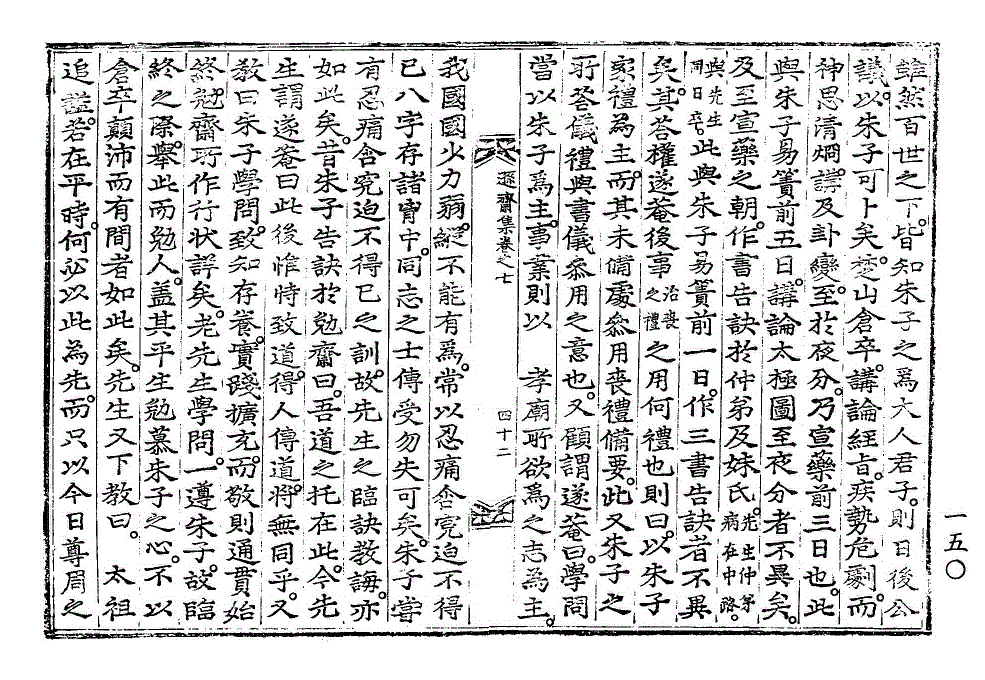 虽然百世之下。皆知朱子之为大人君子。则日后公议。以朱子可卜矣。楚山仓卒。讲论经旨。疾势危剧。而神思清烱。讲及卦变。至于夜分。乃宣药前三日也。此与朱子易箦前五日。讲论太极图至夜分者不异矣。及至宣药之朝。作书告诀于仲弟及妹氏。(先生仲弟病在中路。与先生同日卒。)此与朱子易箦前一日。作三书告诀者不异矣。其答权遂庵后事(治丧之礼)之用何礼也则曰。以朱子家礼为主。而其未备处参用丧礼备要。此又朱子之所答仪礼与书仪参用之意也。又顾谓遂庵曰。学问当以朱子为主。事业则以 孝庙所欲为之志为主。我国国少力弱。纵不能有为。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诸胸中。同志之士传受勿失可矣。朱子尝有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训。故先生之临诀教诲。亦如此矣。昔朱子告诀于勉斋曰。吾道之托在此。今先生谓遂庵曰此后惟恃致道。得人传道。将无同乎。又教曰朱子学问。致知存养。实践扩充。而敬则通贯始终。勉斋所作行状详矣。老先生学问。一遵朱子。故临终之际。举此而勉人。盖其平生勉慕朱子之心。不以仓卒颠沛而有间者如此矣。先生又下教曰。 太祖追谥。若在平时。何必以此为先。而只以今日尊周之
虽然百世之下。皆知朱子之为大人君子。则日后公议。以朱子可卜矣。楚山仓卒。讲论经旨。疾势危剧。而神思清烱。讲及卦变。至于夜分。乃宣药前三日也。此与朱子易箦前五日。讲论太极图至夜分者不异矣。及至宣药之朝。作书告诀于仲弟及妹氏。(先生仲弟病在中路。与先生同日卒。)此与朱子易箦前一日。作三书告诀者不异矣。其答权遂庵后事(治丧之礼)之用何礼也则曰。以朱子家礼为主。而其未备处参用丧礼备要。此又朱子之所答仪礼与书仪参用之意也。又顾谓遂庵曰。学问当以朱子为主。事业则以 孝庙所欲为之志为主。我国国少力弱。纵不能有为。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诸胸中。同志之士传受勿失可矣。朱子尝有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训。故先生之临诀教诲。亦如此矣。昔朱子告诀于勉斋曰。吾道之托在此。今先生谓遂庵曰此后惟恃致道。得人传道。将无同乎。又教曰朱子学问。致知存养。实践扩充。而敬则通贯始终。勉斋所作行状详矣。老先生学问。一遵朱子。故临终之际。举此而勉人。盖其平生勉慕朱子之心。不以仓卒颠沛而有间者如此矣。先生又下教曰。 太祖追谥。若在平时。何必以此为先。而只以今日尊周之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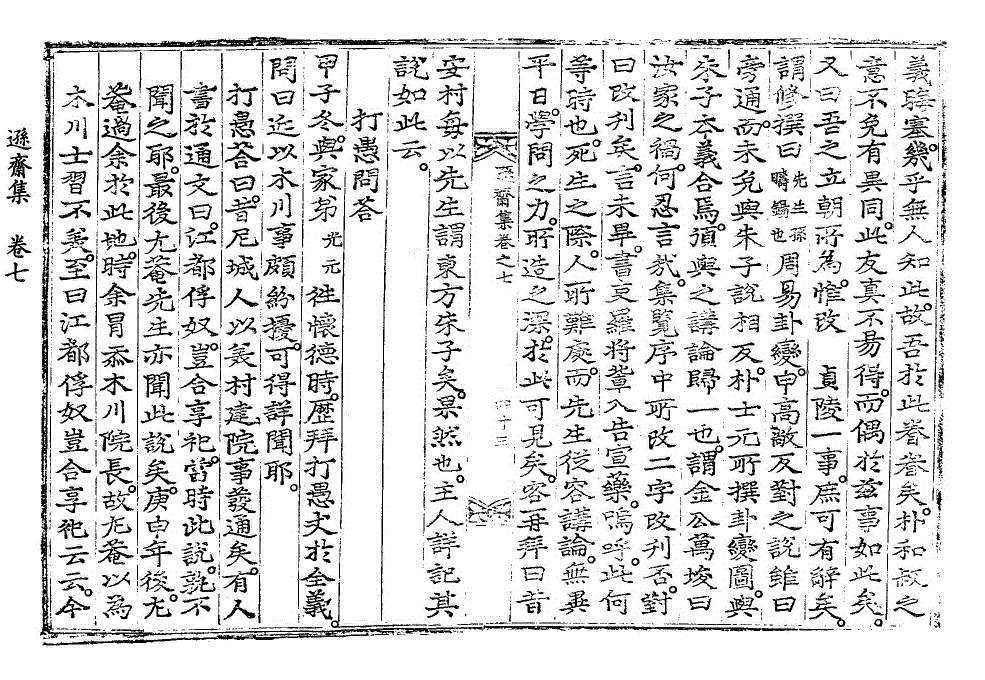 义晦塞。几乎无人知此。故吾于此眷眷矣。朴和叔之意不免有异同。此友真不易得。而偶于玆事如此矣。又曰吾之立朝所为。惟改 贞陵一事。庶可有辞矣。谓修撰曰(先生孙畴锡也)周易卦变。申高敞反对之说虽曰旁通。而未免与朱子说相反。朴士元所撰卦变图。与朱子本义合焉。须与之讲论归一也。谓金公万埈曰汝家之祸。何忍言哉。集览序中所改二字改刊否。对曰改刊矣。言未毕。书吏罗将辈入告宣药。呜呼。此何等时也。死生之际。人所难处。而先生从容讲论。无异平日。学问之力。所造之深。于此可见矣。客再拜曰昔安村每以先生谓东方朱子矣。果然也。主人详记其说如此云。
义晦塞。几乎无人知此。故吾于此眷眷矣。朴和叔之意不免有异同。此友真不易得。而偶于玆事如此矣。又曰吾之立朝所为。惟改 贞陵一事。庶可有辞矣。谓修撰曰(先生孙畴锡也)周易卦变。申高敞反对之说虽曰旁通。而未免与朱子说相反。朴士元所撰卦变图。与朱子本义合焉。须与之讲论归一也。谓金公万埈曰汝家之祸。何忍言哉。集览序中所改二字改刊否。对曰改刊矣。言未毕。书吏罗将辈入告宣药。呜呼。此何等时也。死生之际。人所难处。而先生从容讲论。无异平日。学问之力。所造之深。于此可见矣。客再拜曰昔安村每以先生谓东方朱子矣。果然也。主人详记其说如此云。打愚问答
甲子冬。与家弟(光元)往怀德时。历拜打愚丈于全义。问曰近以木川事颇纷扰。可得详闻耶。
打愚答曰。昔尼城人以美村建院事发通矣。有人书于通文曰。江都俘奴。岂合享祀。当时此说。孰不闻之耶。最后尤庵先生亦闻此说矣。庚申年后。尤庵过余于此地。时余冒忝木川院长。故尤庵以为木川士习不美。至曰江都俘奴岂合享祀云云。今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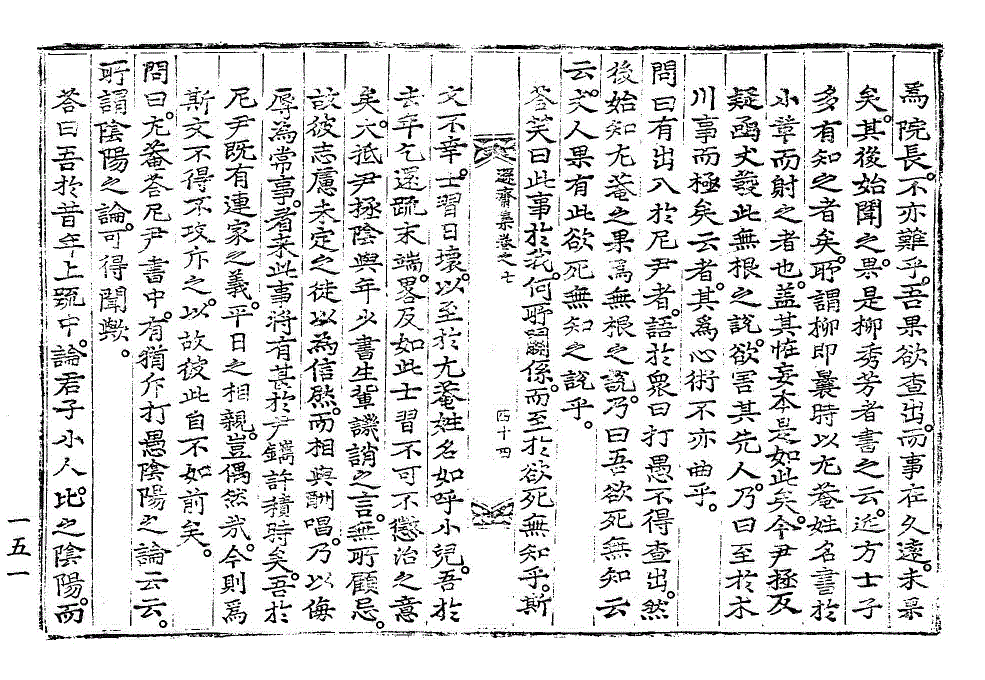 为院长。不亦难乎。吾果欲查出。而事在久远。未果矣。其后始闻之。果是柳秀芳者书之云。近方士子多有知之者矣。所谓柳即曩时以尤庵姓名书于小革而射之者也。盖其怪妄本是如此矣。今尹拯反疑函丈发此无根之说。欲害其先人。乃曰至于木川事而极矣云者。其为心术不亦曲乎。
为院长。不亦难乎。吾果欲查出。而事在久远。未果矣。其后始闻之。果是柳秀芳者书之云。近方士子多有知之者矣。所谓柳即曩时以尤庵姓名书于小革而射之者也。盖其怪妄本是如此矣。今尹拯反疑函丈发此无根之说。欲害其先人。乃曰至于木川事而极矣云者。其为心术不亦曲乎。问曰有出入于尼尹者。语于众曰打愚不得查出。然后始知尤庵之果为无根之说。乃曰吾欲死无知云云。丈人果有此欲死无知之说乎。
答笑曰此事于我。何所关系。而至于欲死无知乎。斯文不幸。士习日坏。以至于尤庵姓名如呼小儿。吾于去年乞还疏末端。略及如此士习不可不惩治之意矣。大抵尹拯阴与年少书生辈讥诮之言。无所顾忌。故彼志虑未定之徒以为信然。而相与酬唱。乃以侮辱为常事。看来此事将有甚于尹镌(一作鑴),许积时矣。吾于尼尹既有连家之义。平日之相亲。岂偶然哉。今则为斯文不得不攻斥之。以故彼此自不如前矣。
问曰。尤庵答尼尹书中。有犹斥打愚阴阳之论云云。所谓阴阳之论。可得闻欤。
答曰吾于昔年上疏中。论君子小人。比之阴阳。而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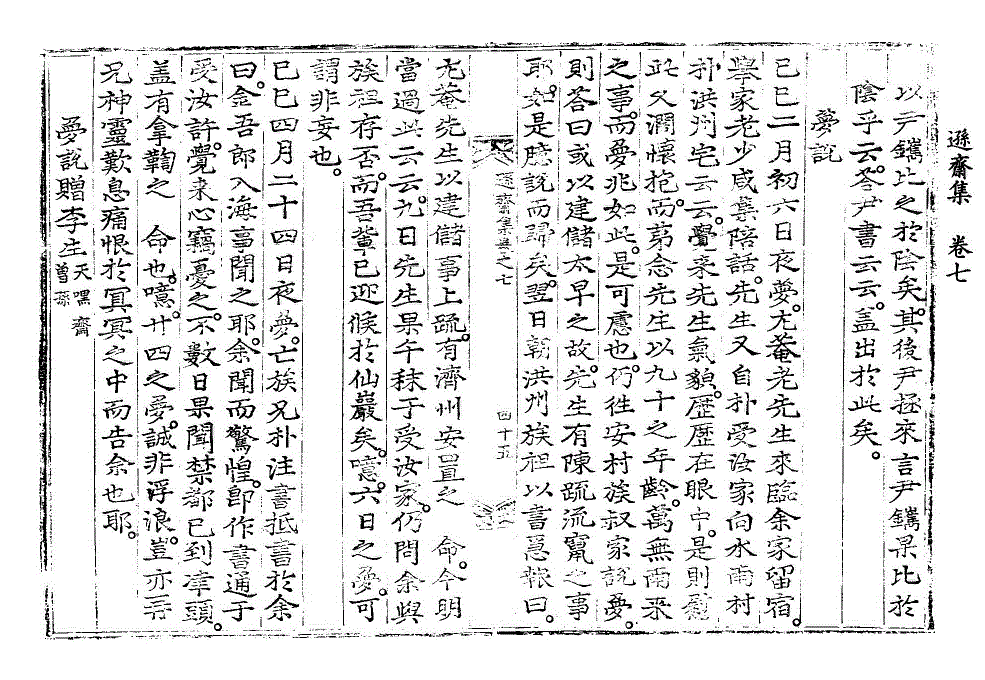 以尹镌(一作鑴)比之于阴矣。其后尹拯来言尹镌(一作鑴)果比于阴乎云。答尹书云云。盖出于此矣。
以尹镌(一作鑴)比之于阴矣。其后尹拯来言尹镌(一作鑴)果比于阴乎云。答尹书云云。盖出于此矣。梦说
己巳二月初六日夜梦。尤庵老先生来临余家留宿。举家老少咸集陪话。先生又自朴受汝家向水南村朴洪州宅云云。觉来先生气貌。历历在眼中。是则慰此久阔怀抱。而第念先生以九十之年龄。万无南来之事。而梦兆如此。是可虑也。仍往安村族叔家说梦。则答曰或以建储太早之故。先生有陈疏流窜之事耶。如是臆说而归矣。翌日朝洪州族袒以书急报曰。尤庵先生以建储事上疏。有济州安置之 命。今明当过此云云。九日先生果午秣于受汝家。仍问余与族袒存否。而吾辈已迎候于仙岩矣。噫。六日之梦。可谓非妄也。
己巳四月二十四日夜梦。亡族兄朴注书抵书于余曰。金吾郎入海事闻之耶。余闻而惊惶。即作书通于受汝许。觉来心窃忧之。不数日果闻禁都已到津头。盖有拿鞫之 命也。噫。廿四之梦。诚非浮浪。岂亦再兄神灵叹息痛恨于冥冥之中而告余也耶。
梦说赠李生(天嘿斋曾孙)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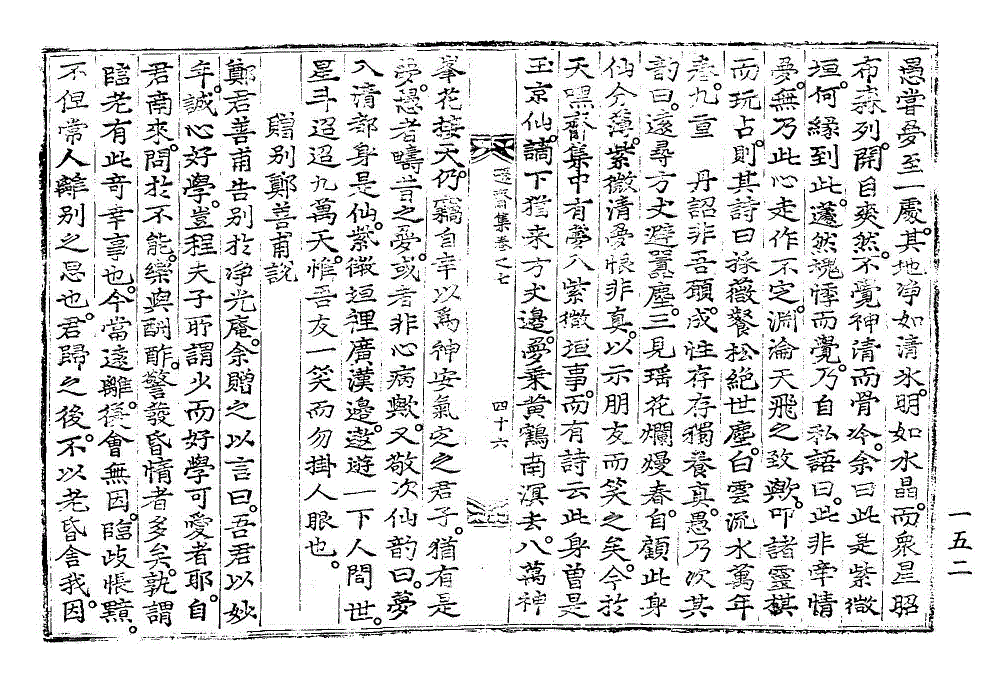 愚尝梦至一处。其地净如清冰。明如水晶。而众星昭布森列。开目爽然。不觉神清而骨冷。余曰此是紫微垣。何缘到此。蘧然魂悸而觉。乃自私语曰。此非牵情梦。无乃此心走作不定。渊沦天飞之致欤。叩诸灵棋而玩占。则其诗曰采薇餐松绝世尘。白云流水万年春。九重 丹诏非吾愿。成性存存独养真。愚乃次其韵曰。远寻方丈避嚣尘。三见瑶花烂熳春。自顾此身仙分薄。紫微清梦恨非真。以示朋友而笑之矣。今于天嘿斋集中有梦入紫微垣事。而有诗云此身曾是玉京仙。谪下犹来方丈边。梦乘黄鹤南溟去。八万神峰花接天。仍窃自幸以为神安气定之君子。犹有是梦。愚者畴昔之梦。或者非心病欤。又敬次仙韵曰。梦入清都身是仙。紫微垣里广汉边。遨游一下人间世。星斗迢迢九万天。惟吾友一笑而勿挂人眼也。
愚尝梦至一处。其地净如清冰。明如水晶。而众星昭布森列。开目爽然。不觉神清而骨冷。余曰此是紫微垣。何缘到此。蘧然魂悸而觉。乃自私语曰。此非牵情梦。无乃此心走作不定。渊沦天飞之致欤。叩诸灵棋而玩占。则其诗曰采薇餐松绝世尘。白云流水万年春。九重 丹诏非吾愿。成性存存独养真。愚乃次其韵曰。远寻方丈避嚣尘。三见瑶花烂熳春。自顾此身仙分薄。紫微清梦恨非真。以示朋友而笑之矣。今于天嘿斋集中有梦入紫微垣事。而有诗云此身曾是玉京仙。谪下犹来方丈边。梦乘黄鹤南溟去。八万神峰花接天。仍窃自幸以为神安气定之君子。犹有是梦。愚者畴昔之梦。或者非心病欤。又敬次仙韵曰。梦入清都身是仙。紫微垣里广汉边。遨游一下人间世。星斗迢迢九万天。惟吾友一笑而勿挂人眼也。赠别郑善甫说
郑君善甫告别于净光庵。余赠之以言曰。吾君以妙年。诚心好学。岂程夫子所谓少而好学可爱者耶。自君南来。问于不能。乐与酬酢。警发昏惰者多矣。孰谓临老有此奇幸事也。今当远离。复会无因。临歧怅黯。不但常人离别之思也。君归之后。不以老昏舍我。因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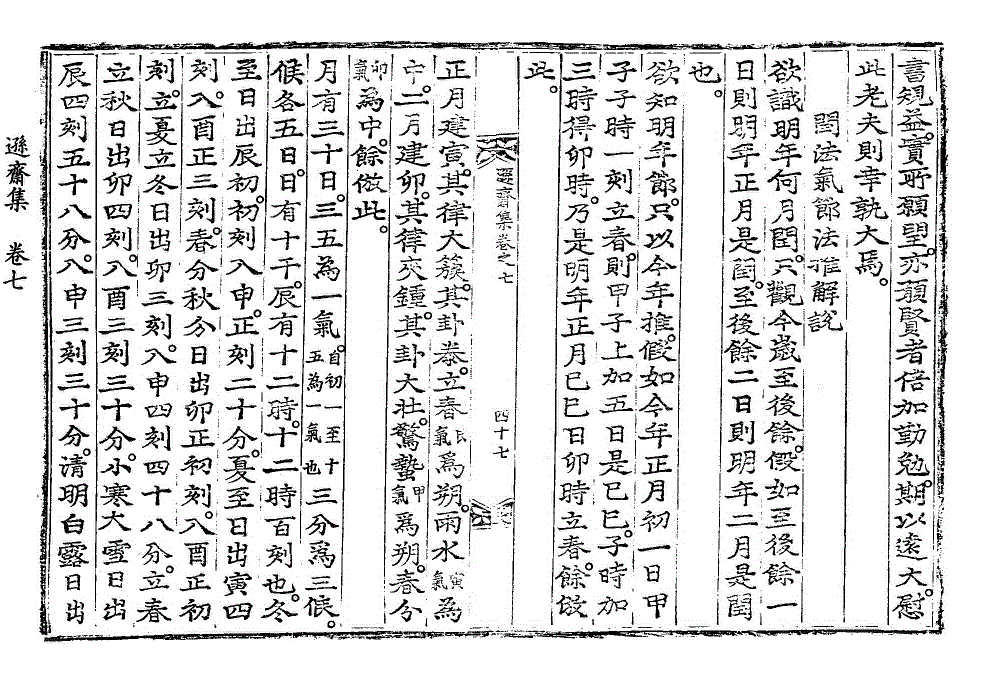 书规益。实所愿望。亦愿贤者倍加勤勉。期以远大。慰此老夫则幸孰大焉。
书规益。实所愿望。亦愿贤者倍加勤勉。期以远大。慰此老夫则幸孰大焉。闰法气节法推解说
欲识明年何月闰。只观今岁至后馀。假如至后馀一日则明年正月是闰。至后馀二日则明年二月是闰也。
欲知明年节。只以今年推。假如今年正月初一日甲子子时一刻立春。则甲子上加五日是己巳。子时加三时得卯时。乃是明年正月己巳日卯时立春。馀仿此。
正月建寅。其律大簇。其卦泰。立春(辰气)为朔。雨水(寅气)为中。二月建卯。其律夹钟。其卦大壮。惊蛰(甲气)为朔。春分(卯气)为中。馀仿此。
月有三十日。三五为一气。(自初一至十五为一气也)三分为三候。候各五日。日有十干。辰有十二时。十二时百刻也。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刻二十分。夏至日出寅四刻。入酉正三刻。春分秋分日出卯正初刻。入酉正初刻。立夏立冬日出卯三刻。入申四刻四十八分。立春立秋日出卯四刻。入酉三刻三十分。小寒大雪日出辰四刻五十八分。入申三刻三十分。清明白露日出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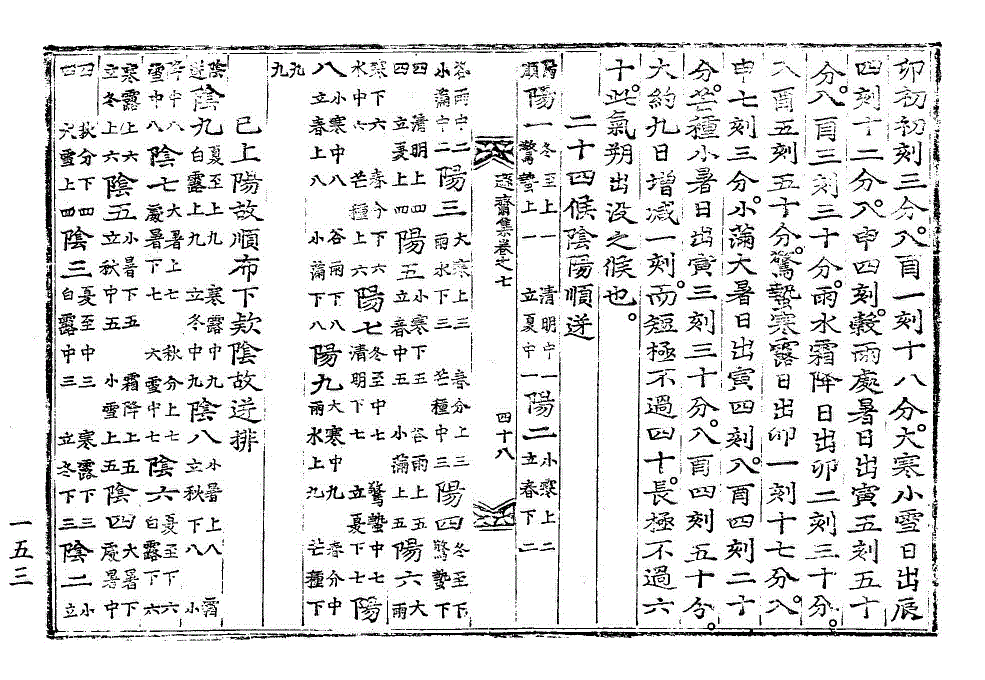 卯初初刻三分。入酉一刻十八分。大寒小雪日出辰四刻十二分。入申四刻。谷雨处暑日出寅五刻五十分。入酉三刻三十分。雨水霜降日出卯二刻三十分。入酉五刻五十分。惊蛰寒露日出卯一刻十七分。入申七刻三分。小满大暑日出寅四刻。入酉四刻二十分。芒种小暑日出寅三刻三十分。入酉四刻五十分。大约九日增减一刻。而短极不过四十。长极不过六十。此气朔出没之候也。
卯初初刻三分。入酉一刻十八分。大寒小雪日出辰四刻十二分。入申四刻。谷雨处暑日出寅五刻五十分。入酉三刻三十分。雨水霜降日出卯二刻三十分。入酉五刻五十分。惊蛰寒露日出卯一刻十七分。入申七刻三分。小满大暑日出寅四刻。入酉四刻二十分。芒种小暑日出寅三刻三十分。入酉四刻五十分。大约九日增减一刻。而短极不过四十。长极不过六十。此气朔出没之候也。二十四候阴阳顺逆
(阳顺)阳一(冬至上一惊蛰上一 清明中一立夏中一)阳二(小寒上二立春下二 谷雨中二小满中二)阳三(大寒上三雨水下三 春分上三芒种中三)阳四(冬至下四惊蛰下四 清明上四立夏上四)阳五(小寒下五立春中五 谷雨上五小满上五)阳六(大寒下六雨水中六 春分下六芒种上六)阳七(冬至中七清明下七 惊蛰中七立夏下七)阳八(小寒中八立春上八 谷雨下八小满下八)阳九(大寒中九雨水上九 春分中九芒种下九)
已上阳故顺布下款阴故逆排
(阴逆)阴九(夏至上九白露上九 寒露中九立冬中九)阴八(小暑上八立秋下八 霜降中八小雪中八)阴七(大暑上七处暑下七 秋分上七大雪中七)阴六(夏至下六白露下六 寒露上六立冬上六)阴五(小暑下五立秋中五 霜降上五小雪上五)阴四(大暑下四处暑中四 秋分下四大雪上四)阴三(夏至中三白露中三 寒露下三立冬下三)阴二(小暑中二立秋上二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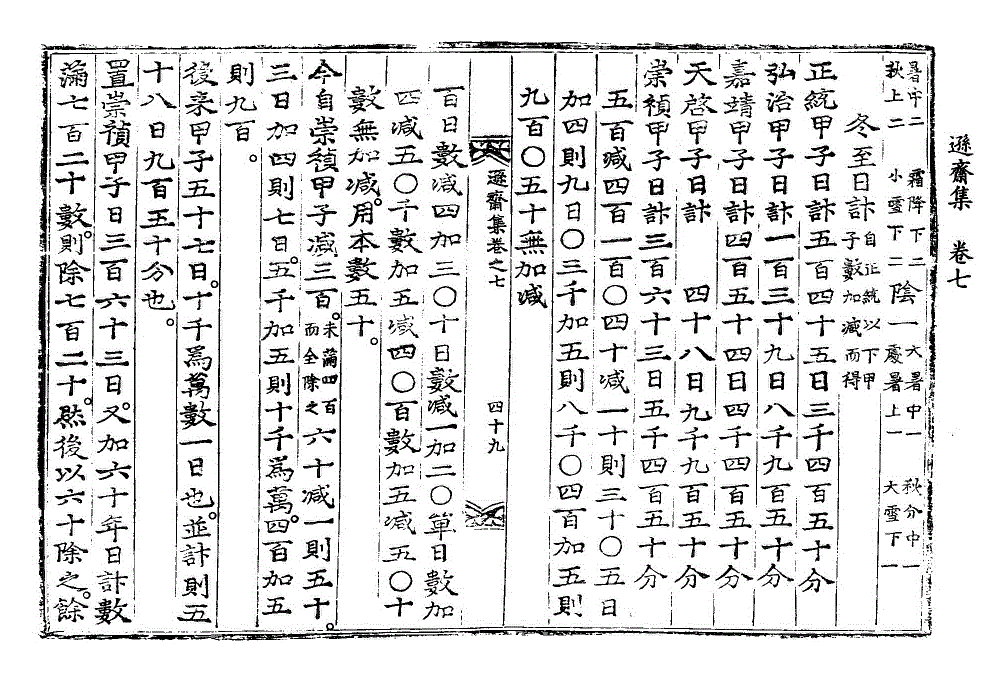 霜降下二小雪下二)阴一(大暑中一处暑上一 秋分中一大雪下一)
霜降下二小雪下二)阴一(大暑中一处暑上一 秋分中一大雪下一)冬至日计(自正统以下甲子数加减而得)
正统甲子日计五百四十五日三千四百五十分
弘治甲子日计一百三十九日八千九百五十分
嘉靖甲子日计四百五十四日四千四百五十分
天启甲子日计 四十八日九千九百五十分
崇祯甲子日计三百六十三日五千四百五十分
五百减四百一百○四十减一十则三十○五日加四则九日○三千加五则八千○四百加五则九百○五十无加减
百日数减四加三○十日数减一加二○单日数加四减五○千数加五减四○百数加五减五○十数无加减。用本数五十。
今自崇祯甲子减三百。(未满四百而全除之)六十减一则五十。三日加四则七日。五千加五则十千为万。四百加五则九百。
后来甲子五十七日。十千为万数一日也。并计则五十八日九百五十分也。
置崇祯甲子日三百六十三日。又加六十年日计数满七百二十数。则除七百二十。然后以六十除之。馀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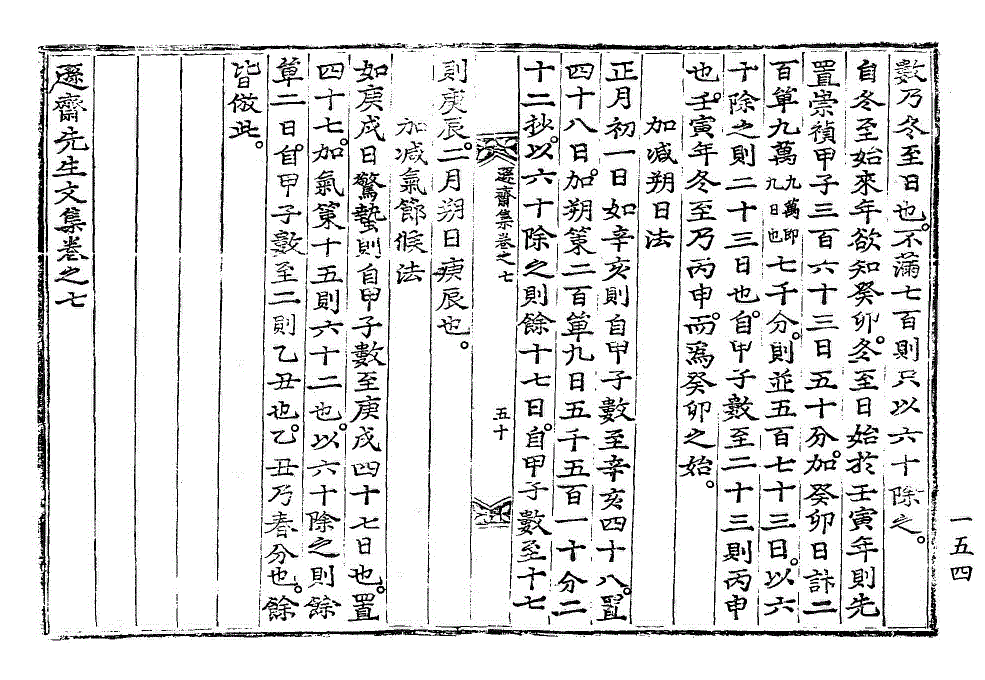 数乃冬至日也。不满七百则只以六十除之。
数乃冬至日也。不满七百则只以六十除之。自冬至始来年欲知癸卯。冬至日始于壬寅年则先置崇祯甲子三百六十三日五十分。加癸卯日计二百单九万(九万即九日也)七千分。则并五百七十三日。以六十除之则二十三日也。自甲子数至二十三则丙申也。壬寅年冬至乃丙申。而为癸卯之始。
加减朔日法
正月初一日如辛亥则自甲子数至辛亥四十八。置四十八日。加朔策二百单九日五千五百一十分二十二抄。以六十除之则馀十七日。自甲子数至十七则庚辰。二月朔日庚辰也。
加减气节候法
如庚戌日惊蛰则自甲子数至庚戌四十七日也。置四十七。加气策十五则六十二也。以六十除之则馀单二日。自甲子数至二则乙丑也。乙丑乃春分也。馀皆仿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