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书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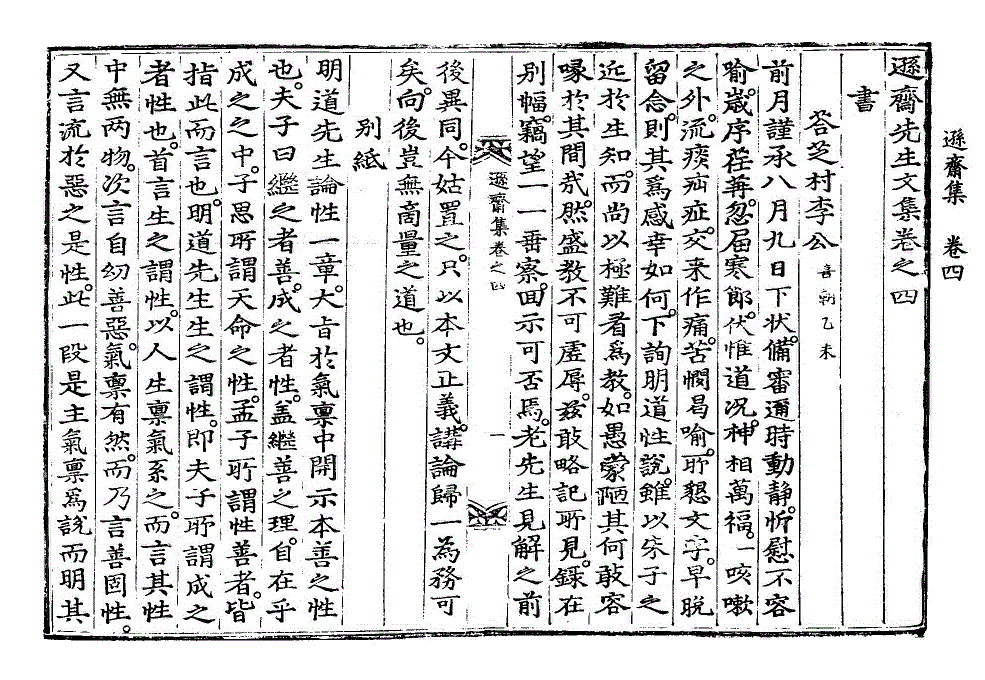 答芝村李公(喜朝○乙未)
答芝村李公(喜朝○乙未)前月谨承八月九日下状。备审迩时动静。忻慰不容喻。岁序荏苒。忽届寒节。伏惟道况。神相万福。一咳嗽之外。流痰疝症。交来作痛。苦悯曷喻。所恳文字。早晚留念。则其为感幸如何。下询明道性说。虽以朱子之近于生知。而尚以极难看为教。如愚蒙陋其何敢容喙于其间哉。然盛教不可虚辱。玆敢略记所见。录在别幅。窃望一一垂察。回示可否焉。老先生见解之前后异同。今姑置之。只以本文正义。讲论归一为务可矣。向后岂无商量之道也。
别纸
明道先生论性一章。大旨于气禀中开示本善之性也。夫子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盖继善之理。自在乎成之之中。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者。皆指此而言也。明道先生生之谓性。即夫子所谓成之者性也。首言生之谓性。以人生禀气系之。而言其性中无两物。次言自幼善恶。气禀有然。而乃言善固性。又言流于恶之是性。此一段是主气禀为说而明其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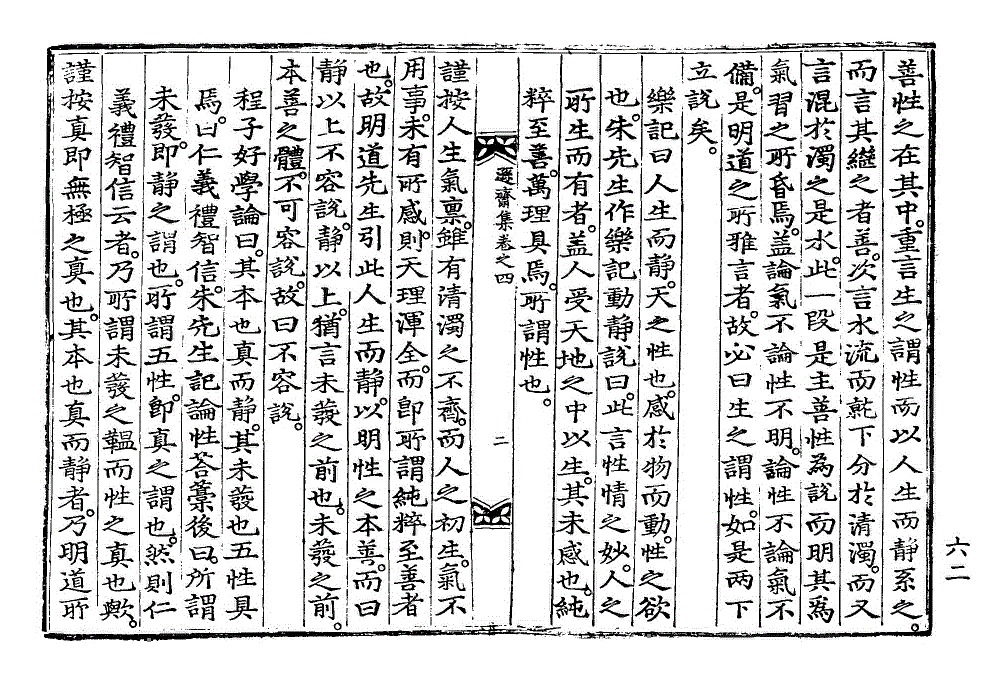 善性之在其中。重言生之谓性而以人生而静系之。而言其继之者善。次言水流而就下分于清浊。而又言混于浊之是水。此一段是主善性为说而明其为气习之所昏焉。盖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是明道之所雅言者。故必曰生之谓性。如是两下立说矣。
善性之在其中。重言生之谓性而以人生而静系之。而言其继之者善。次言水流而就下分于清浊。而又言混于浊之是水。此一段是主善性为说而明其为气习之所昏焉。盖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是明道之所雅言者。故必曰生之谓性。如是两下立说矣。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先生作乐记动静说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纯粹至善。万理具焉。所谓性也。
谨按人生气禀。虽有清浊之不齐。而人之初生。气不用事。未有所感。则天理浑全。而即所谓纯粹至善者也。故明道先生引此人生而静。以明性之本善。而曰静以上不容说。静以上。犹言未发之前也。未发之前。本善之体。不可容说。故曰不容说。
程子好学论曰。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朱先生记论性答藁后曰。所谓未发。即静之谓也。所谓五性。即真之谓也。然则仁义礼智信云者。乃所谓未发之鞰(一作韫)而性之真也欤。
谨按真即无极之真也。其本也真而静者。乃明道所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3H 页
 引人生而静之谓也。方其静也。真体具焉。此亦纯粹至善之意也。
引人生而静之谓也。方其静也。真体具焉。此亦纯粹至善之意也。中庸章句曰未发即性也。中庸或问曰方其未发也。浑然在中。无所偏倚。故曰中。以其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该。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谨按未发即所谓静也。以上诸说。皆言人生而静时。天性之纯粹至善者。浑然在中矣。
朱子答严时亨书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又曰谗谓之性。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体。
谨按既曰静是未发时。又曰不全是性之本体。此与乐记好学论中庸章句或问诸说。无乃大相径庭欤。况人生而静时。不是性之本体。则继之者善。从何而发也。未发之前。四德全具。纯粹至善。所以继之者善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只是说三字最宜玩味。盖曰未发之性。不可容说。故说性者只是说继之者善而已。孟子之因其四端之发见而明其本体之善者此也。明道之意恐是如此。而朱先生答严一书。参之诸说。求之本文。而终未能晓然。此甚懑然。望于此处大着心眼如何。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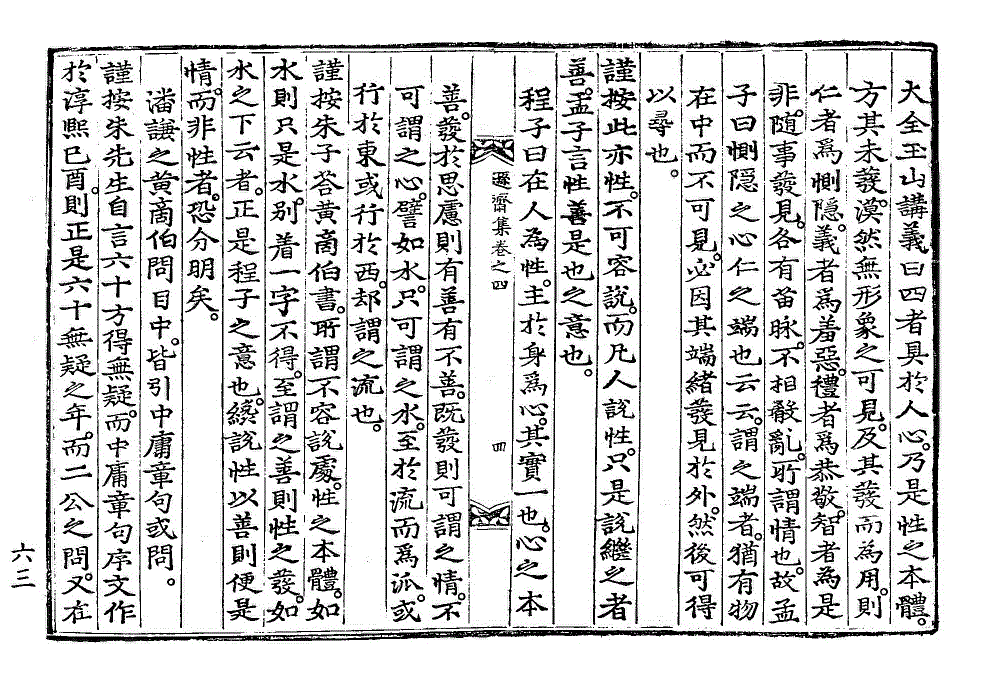 大全玉山讲义曰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云云。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以寻也。
大全玉山讲义曰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云云。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以寻也。谨按此亦性。不可容说。而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之意也。
程子曰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之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可谓之水。至于流而为派。或行于东或行于西。却谓之流也。
谨按朱子答黄商伯书。所谓不容说处。性之本体。如水则只是水。别着一字不得。至谓之善则性之发。如水之下云者。正是程子之意也。才说性以善则便是情。而非性者。恐分明矣。
潘谦之黄商伯问目中。皆引中庸章句或问。
谨按朱先生自言六十方得无疑。而中庸章句序文作于淳熙己酉。则正是六十无疑之年。而二公之问。又在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4H 页
 章句或问既成之后。其答潘黄书。恐未可谓初年见解也。
章句或问既成之后。其答潘黄书。恐未可谓初年见解也。答黄商伯第三书。言仪礼丧服传疏。而曰往时妄论。亦未见此。归乃得之云云。
谨按光宗元年庚戌也。当时不能袭位而执丧。故先生上劄论嫡孙代之执丧。归后得见赵商与郑康成问答一段。答黄书以往时为言。则第三书分明辛亥以后之书。而论性说问答又在其后。则盖去先生易箦之年庚申未远也。其非初年见解。此亦可證也。
答杜仁仲书曰孟子论性。只以情可为善为说。盖此发用处。便见本原之至善。不待别求。若可别求则是人生而静以上却容说也。孟子所论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亦是此意也。
谨按此亦与答潘黄书一义也。大抵潘黄杜诸书及论性说。皆是先生之手自笔之于书者。而异乎门人所记。则诸说不应皆误。而答严一书独与此异。且曰以本文论之。皆不可晓。乃以忘言会意为教。则亦异于论性说之明白辨说。莫或初年见解而然欤。
答芝村(丙申)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4L 页
 恭承初二日惠书。谨审伊时静候万福。区区欣慰。不容名喻。所恳幽堂文字铭念搆下。感激不知所以为谢也。一咳症挟凉增苦。苦悯奈何。向来斯文之祸。将无所不至。 天鉴孔昭。是非明正。士林之庆幸孰大于是耶。别纸勤教至此。警发昧陋者多矣。第不能无疑于其间。有此反复。因便回示。千万之望。
恭承初二日惠书。谨审伊时静候万福。区区欣慰。不容名喻。所恳幽堂文字铭念搆下。感激不知所以为谢也。一咳症挟凉增苦。苦悯奈何。向来斯文之祸。将无所不至。 天鉴孔昭。是非明正。士林之庆幸孰大于是耶。别纸勤教至此。警发昧陋者多矣。第不能无疑于其间。有此反复。因便回示。千万之望。别纸
性即理也。在天为理。在人为性。故夫子曰成之者性。明道先生曰生之为性。盖于禀受中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兼气质而言曰气质之性。固非有两性。而人生而静时。天性浑然全具矣。今曰人物未生时。未可名为性。人生而静。说性时不是性云尔。则记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云者。果何谓也。伊川所谓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者。又何谓也。朱先生答潘黄杜诸说与答严陈王诸书及语类不同者。莫或有所以也欤。先生又特著明道先生论性说一篇。发明明道之说极为明白。盖此一篇说。安知非中和旧说序文之类欤。大抵明道之说。从初至终。皆是明其气禀中有善性之义。岂于中间乃引人生而静之句。而犹曰不是性之本体也哉。若曰人生而静时。性非本体。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5H 页
 则中庸未发之说。孟子性善之论。皆未免为驾虚之谈。而朱先生后来用十分精力。许多发明大本之说。尽归于无用之空谈。此愚之所以懑然者也。盖人生而后。方可谓性。而人生而静则天性全矣。然若欲专言其性则政所谓无极之真而不容说者也。若言其善则已是情而非性也。故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如是见解则明道之说。顺而不碍。无毫发可疑。朱先生所著明道论性说一篇。可不熟读而详味之哉。此非末学浅见所敢容喙处。而敢言至此。不胜兢惶。幸乞宽其诛而虚心垂察焉。昔年面禀于老先生时。先生以缠绕极难看为教矣。老先生答先人书。遂庵之说未知果得老先生之意否。正从前鄙意所在语句如何。遂翁未见先人问目故云云乃尔耶。
则中庸未发之说。孟子性善之论。皆未免为驾虚之谈。而朱先生后来用十分精力。许多发明大本之说。尽归于无用之空谈。此愚之所以懑然者也。盖人生而后。方可谓性。而人生而静则天性全矣。然若欲专言其性则政所谓无极之真而不容说者也。若言其善则已是情而非性也。故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如是见解则明道之说。顺而不碍。无毫发可疑。朱先生所著明道论性说一篇。可不熟读而详味之哉。此非末学浅见所敢容喙处。而敢言至此。不胜兢惶。幸乞宽其诛而虚心垂察焉。昔年面禀于老先生时。先生以缠绕极难看为教矣。老先生答先人书。遂庵之说未知果得老先生之意否。正从前鄙意所在语句如何。遂翁未见先人问目故云云乃尔耶。答芝村
朱子答余正甫书白衣布带燕居之服。遂庵断以为复古之渐。而区区愚见则朱子既言其练禫之节。注又言其制古丧服。则白衣布带。明是燕居之服。而非通言之者也。若以白衣布带为正服。而谓复古之渐。则既是白衣。宁有可练之节耶。愚见如是。未知高明以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5L 页
 为如何。
为如何。芝村答书
斯文不幸。吾党无禄。遂翁奄忽捐馆恸矣。尚何言哉。在逝者寿福兼备。宁有馀憾。只此后死之悲。无以自堪。窃惟尊兄亦应同此怀也。仍惟秋高霜冷。味道起居增相。不得承候。以过半年。每欲一书。而亦有所待者。以致一向迁就。岂胜怅叹。此间衰惫日加。放废益甚。重以一家丧病连仍。了无一分意况。只自怜叹而已。向来往复事。仍季兄获见兄与遂庵书牍。意兄必更有所禀。欲知其毕境(一作竟)出场如何然后仰复。其所待者此也。然既不能有闻。前月李台行亦得书。略论此事。谓区区以宋孝宗时群臣谓皆同服衰。槩不免错认鄙意也。念其病患。诚难极意讲论。然欲早晚一明其不然矣。书来未数日。遽承凶音。此亦终未归一。遂成遗恨。尤可悲也。从此论亦无益。欲不复云云。前惠别纸。岂胜佩幸。盛见一如鄙意。更无可论者。夏间见遂庵答高明书后。略有一书于季氏矣。此论未得归一。良可咄叹。而只兄与弟所见相合。此为甚幸耳。
与松岩奇公(挺翼○辛酉)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H 页
 节届初夏。伏不审道体何如。伏慕区区不任下诚。昨者伏见答家严书。始审惟忧非细。向虑无已。今已有勿药之喜耶。第书中极以听言之难为戒。则侍生之所听于尊丈。而游谈朋友归告家亲者。毕竟非尊丈之本意而误传者耶。惶骇汗蹙。不知所喻。日者几席之间。从容答问之际。以此性烱然不乱寂然不动而不偏不倚者。谓之未发之中者。侍生之说也。以其无穷无限。生生不已之理。常在方寸之中者。谓之未发之中者。尊丈之教也。以故尊丈又下教曰。不但众人有未发之中。禽兽亦有未发之中矣。侍生对曰以程朱之说观之。则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不偏于喜不倚于乐。惺惺无昏昧之失。寂寂无纷起之念。然后方可谓之未发之中也。众人则不然。不偏于喜则倚于怒。不倚于怒则偏于乐。以至于物欲动荡。未尝暂有宁息之时。恐不可谓有未发也。然尊丈之见则以生生不穷之理。恒在方寸者。谓之大本。故并以众人禽兽皆以为有大本。而大异于侍生之认得个中字者也。尊丈又下教曰性即理也。众人不可谓之无性也。既谓之有性则有未发也。喜情虽发。而犹有可怒之性。推之七情。莫不皆然。则何可谓无未发也。设使
节届初夏。伏不审道体何如。伏慕区区不任下诚。昨者伏见答家严书。始审惟忧非细。向虑无已。今已有勿药之喜耶。第书中极以听言之难为戒。则侍生之所听于尊丈。而游谈朋友归告家亲者。毕竟非尊丈之本意而误传者耶。惶骇汗蹙。不知所喻。日者几席之间。从容答问之际。以此性烱然不乱寂然不动而不偏不倚者。谓之未发之中者。侍生之说也。以其无穷无限。生生不已之理。常在方寸之中者。谓之未发之中者。尊丈之教也。以故尊丈又下教曰。不但众人有未发之中。禽兽亦有未发之中矣。侍生对曰以程朱之说观之。则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不偏于喜不倚于乐。惺惺无昏昧之失。寂寂无纷起之念。然后方可谓之未发之中也。众人则不然。不偏于喜则倚于怒。不倚于怒则偏于乐。以至于物欲动荡。未尝暂有宁息之时。恐不可谓有未发也。然尊丈之见则以生生不穷之理。恒在方寸者。谓之大本。故并以众人禽兽皆以为有大本。而大异于侍生之认得个中字者也。尊丈又下教曰性即理也。众人不可谓之无性也。既谓之有性则有未发也。喜情虽发。而犹有可怒之性。推之七情。莫不皆然。则何可谓无未发也。设使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L 页
 七情俱发。未发之中则犹在于方寸矣。时庭玉贤兄从傍禀扣曰。中庸既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云尔。而今曰七情俱发而犹有未发之中云。则似有异于中庸本文之义云云。而侍生亦不能解惑而退。其时答问次第。如右所陈者。故来时暂见金德章而略言其槩矣。未知厥后德章何以为说也。伏乞开示。以解惶惧之意幸甚。
七情俱发。未发之中则犹在于方寸矣。时庭玉贤兄从傍禀扣曰。中庸既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云尔。而今曰七情俱发而犹有未发之中云。则似有异于中庸本文之义云云。而侍生亦不能解惑而退。其时答问次第。如右所陈者。故来时暂见金德章而略言其槩矣。未知厥后德章何以为说也。伏乞开示。以解惶惧之意幸甚。与松岩(辛酉)
前日进拜时下教曰。众人虽无未发之中。而大本则犹存在里面。退而思之。殆忘寝食。而终未见符合于先儒发明子思之本旨者。玆敢略陈童观。以求至教。伏乞垂察焉。盖事物未至。思虑未萌。则天命之性。真体全具。而亭亭当当。不偏不倚。是乃中也大本也。故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子曰未感于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为天下之大本也。考之中庸。参之考亭。而未见其无未发而有大本之意也。盖详尊丈之意。以为喜情未发。可怒则怒。若无此怒之根本。则怒无所发出也。乃有云云之教矣。然侍生之所认大本者。盖天命之性。不为气禀物欲之蔽。而鉴空衡平。不偏不倚。其体至静而无所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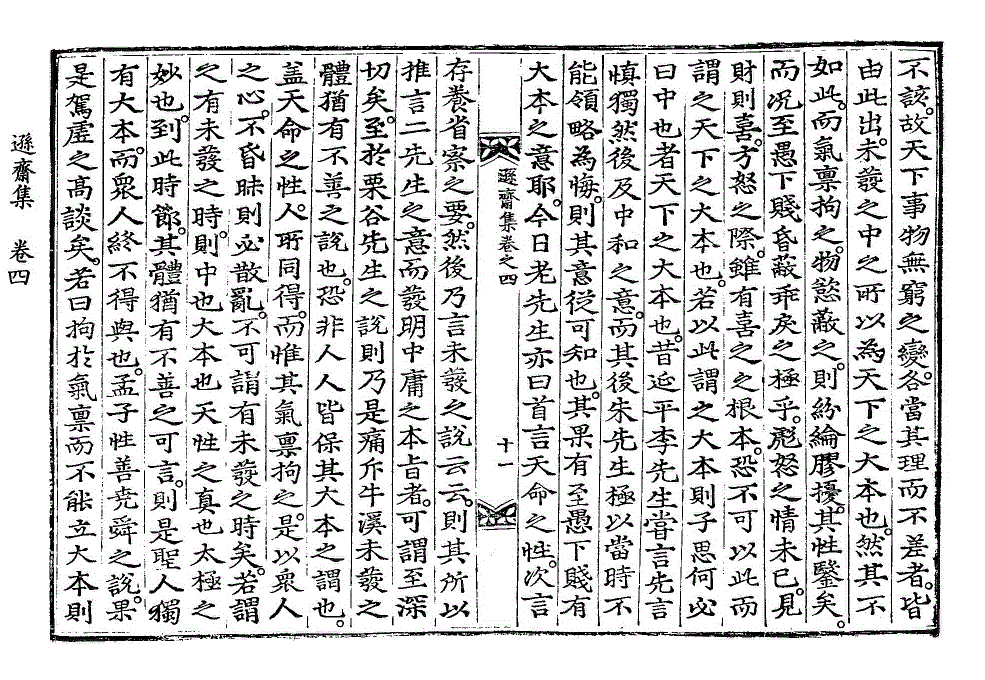 不该。故天下事物无穷之变。各当其理而不差者。皆由此出。未发之中之所以为天下之大本也。然其不如此。而气禀拘之。物欲蔽之。则纷纶胶扰。其性凿矣。而况至愚下贱昏蔽乖戾之极乎。彪怒之情未已。见财则喜。方怒之际。虽有喜之之根本。恐不可以此而谓之天下之大本也。若以此谓之大本则子思何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昔延平李先生尝言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之意。而其后朱先生极以当时不能领略为悔。则其意从可知也。其果有至愚下贱有大本之意耶。今日老先生亦曰首言天命之性。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然后乃言未发之说云云。则其所以推言二先生之意而发明中庸之本旨者。可谓至深切矣。至于栗谷先生之说则乃是痛斥牛溪未发之体犹有不善之说也。恐非人人皆保其大本之谓也。盖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而惟其气禀拘之。是以众人之心。不昏昧则必散乱。不可谓有未发之时矣。若谓之有未发之时。则中也大本也天性之真也太极之妙也。到此时节。其体犹有不善之可言。则是圣人独有大本。而众人终不得与也。孟子性善尧舜之说。果是驾虚之高谈矣。若曰拘于气禀而不能立大本则
不该。故天下事物无穷之变。各当其理而不差者。皆由此出。未发之中之所以为天下之大本也。然其不如此。而气禀拘之。物欲蔽之。则纷纶胶扰。其性凿矣。而况至愚下贱昏蔽乖戾之极乎。彪怒之情未已。见财则喜。方怒之际。虽有喜之之根本。恐不可以此而谓之天下之大本也。若以此谓之大本则子思何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昔延平李先生尝言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之意。而其后朱先生极以当时不能领略为悔。则其意从可知也。其果有至愚下贱有大本之意耶。今日老先生亦曰首言天命之性。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然后乃言未发之说云云。则其所以推言二先生之意而发明中庸之本旨者。可谓至深切矣。至于栗谷先生之说则乃是痛斥牛溪未发之体犹有不善之说也。恐非人人皆保其大本之谓也。盖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而惟其气禀拘之。是以众人之心。不昏昧则必散乱。不可谓有未发之时矣。若谓之有未发之时。则中也大本也天性之真也太极之妙也。到此时节。其体犹有不善之可言。则是圣人独有大本。而众人终不得与也。孟子性善尧舜之说。果是驾虚之高谈矣。若曰拘于气禀而不能立大本则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L 页
 可也。谓之有未发而犹有恶之萌兆则大不可矣。栗谷先生之意。盖如此矣。于此亦未见中与大本分作两端看也。伏乞下赐一语。开此昏蒙之惑何如。
可也。谓之有未发而犹有恶之萌兆则大不可矣。栗谷先生之意。盖如此矣。于此亦未见中与大本分作两端看也。伏乞下赐一语。开此昏蒙之惑何如。与松岩(辛酉五月)
顷承众人下愚。虽无未发之中。犹存大本之教。而于私心不能无疑。故日者族兄之去。敢呈瞽说矣。乃蒙不鄙。还赐教答。迄不胜感戢之至。第侍生于此等说话。盖尝自以为主理而言矣。下书反有遗却理一边之教。此岂侍生之说。辞不达意而然欤。盖未发者。寂然不动。十分宁静底时节也。于此时节。天命之性。当体全具。而浑然在中。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又谓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然则大本之所以得名者。以其中也。天性之全。其本体也静而无不该也。众人之心。既谓之无未发之中。则不可谓常存大本也。何可谓无未发而犹能存此大本也。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以中与大本为一也。今曰虽无未发之中。犹存大本。则是以中与大本为二。而别求大本于中之外也。恐有违于子思垂训之本旨矣。大抵性则理也。众人下愚同得于禀生之初。而惟其气质杂糅而物欲动荡。未尝暂有宁息之时。而至于梦寐之间。亦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H 页
 且颠倒。则何时寂然不动。肃然不乱。而存此天理之全体也。是故朱子曰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于动。又曰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此非分明易见之训乎。自其未发之中观之。则大本固是天性之全体。而自其不能宁静纷纶胶扰者观之。则天性已差而体常不立。不可谓之大本也。故朱子曰乐记直到好恶无节处。方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殊不知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后差也。又曰不能慎独则虽事物未至。固已纷纶胶扰。无复未发之时。既无以致夫所谓中。而其发必乖。又无以致夫所谓和。惟其戒谨恐惧。不敢须臾离。然后中和可致。而大本达道乃在我。朱子此训皆何谓也。众人下愚之不能存大本者。于此亦可见矣。朱子初年与南轩书曰。性未尝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政尊丈怒心未已。遇哀则哀。是常有大本之说也。然其后朱子自注此书曰。此书所论尤乖戾云。伏乞于此更加垂察。以牗昏蒙之惑。幸甚幸甚。
且颠倒。则何时寂然不动。肃然不乱。而存此天理之全体也。是故朱子曰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于动。又曰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此非分明易见之训乎。自其未发之中观之。则大本固是天性之全体。而自其不能宁静纷纶胶扰者观之。则天性已差而体常不立。不可谓之大本也。故朱子曰乐记直到好恶无节处。方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殊不知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后差也。又曰不能慎独则虽事物未至。固已纷纶胶扰。无复未发之时。既无以致夫所谓中。而其发必乖。又无以致夫所谓和。惟其戒谨恐惧。不敢须臾离。然后中和可致。而大本达道乃在我。朱子此训皆何谓也。众人下愚之不能存大本者。于此亦可见矣。朱子初年与南轩书曰。性未尝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政尊丈怒心未已。遇哀则哀。是常有大本之说也。然其后朱子自注此书曰。此书所论尤乖戾云。伏乞于此更加垂察。以牗昏蒙之惑。幸甚幸甚。答房大汝(斗天○辛未)
道字之辨。来说虽多。而只是旧来说话。而其中又有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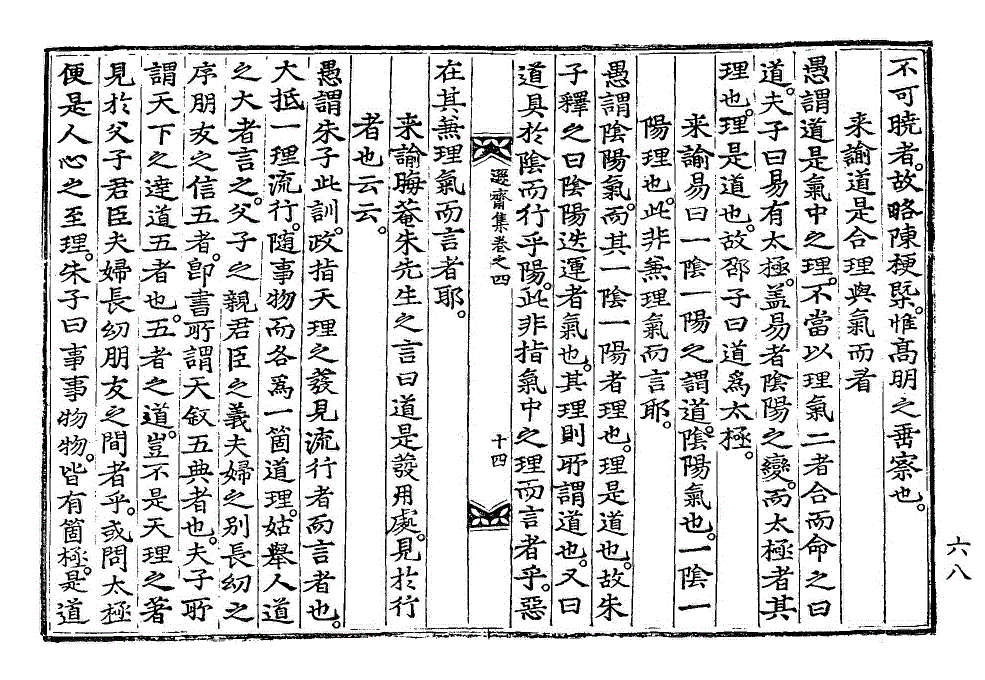 不可晓者。故略陈梗槩。惟高明之垂察也。
不可晓者。故略陈梗槩。惟高明之垂察也。来谕道是合理与气而看
愚谓道是气中之理。不当以理气二者合而命之曰道。夫子曰易有太极。盖易者阴阳之变。而太极者其理也。理是道也。故邵子曰道为太极。
来谕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一阴一阳理也。此非兼理气而言耶。
愚谓阴阳气。而其一阴一阳者理也。理是道也。故朱子释之曰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也。又曰道具于阴而行乎阳。此非指气中之理而言者乎。恶在其兼理气而言者耶。
来谕晦庵朱先生之言曰道是发用处。见于行者也云云。
愚谓朱子此训。政指天理之发见流行者而言者也。大抵一理流行。随事物而各为一个道理。姑举人道之大者言之。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即书所谓天叙五典者也。夫子所谓天下之达道五者也。五者之道。岂不是天理之著见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者乎。或问太极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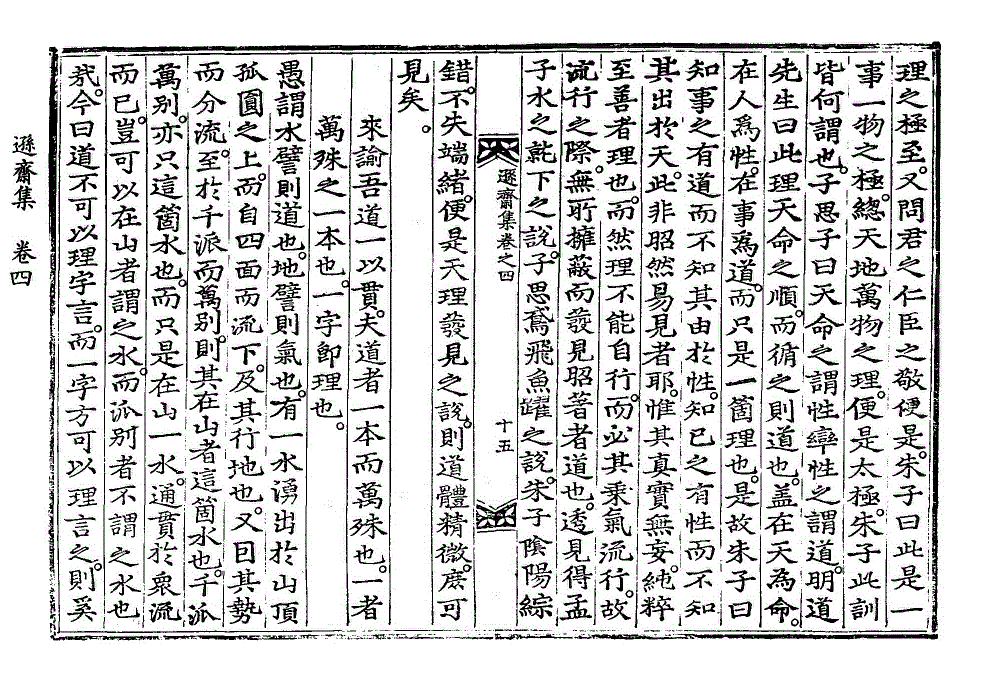 理之极至。又问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朱子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此训皆何谓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明道先生曰此理天命之顺。而循之则道也。盖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事为道。而只是一个理也。是故朱子曰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此非昭然易见者耶。惟其真实无妄。纯粹至善者理也。而然理不能自行。而必其乘气流行。故流行之际。无所拥蔽而发见昭著者道也。透见得孟子水之就下之说。子思鸢飞鱼跃之说。朱子阴阳综错。不失端绪。便是天理发见之说。则道体精微。庶可见矣。
理之极至。又问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朱子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此训皆何谓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明道先生曰此理天命之顺。而循之则道也。盖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事为道。而只是一个理也。是故朱子曰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此非昭然易见者耶。惟其真实无妄。纯粹至善者理也。而然理不能自行。而必其乘气流行。故流行之际。无所拥蔽而发见昭著者道也。透见得孟子水之就下之说。子思鸢飞鱼跃之说。朱子阴阳综错。不失端绪。便是天理发见之说。则道体精微。庶可见矣。来谕吾道一以贯。夫道者一本而万殊也。一者万殊之一本也。一字即理也。
愚谓水譬则道也。地譬则气也。有一水涌出于山顶孤圆之上。而自四面而流下。及其行地也。又因其势而分流。至于千派而万别。则其在山者这个水也。千派万别。亦只这个水也。而只是在山一水。通贯于众流而已。岂可以在山者谓之水。而派别者不谓之水也哉。今曰道不可以理字言。而一字方可以理言之。则奚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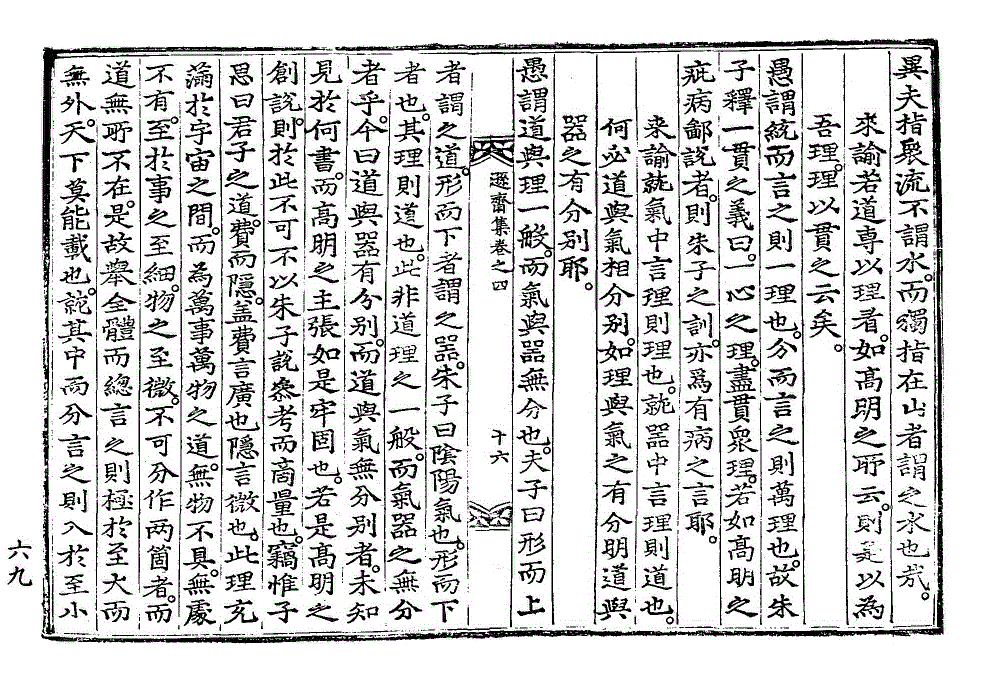 异夫指众流不谓水。而独指在山者谓之水也哉。
异夫指众流不谓水。而独指在山者谓之水也哉。来谕若道专以理看。如高明之所云。则是以为吾理。理以贯之云矣。
愚谓统而言之则一理也。分而言之则万理也。故朱子释一贯之义曰。一心之理。尽贯众理。若如高明之疵病鄙说者。则朱子之训。亦为有病之言耶。
来谕就气中言理则理也。就器中言理则道也。何必道与气相分别。如理与气之有分明道与器之有分别耶。
愚谓道与理一般。而气与器无分也。夫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子曰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其理则道也。此非道理之一般。而气器之无分者乎。今曰道与器有分别。而道与气无分别者。未知见于何书。而高明之主张如是牢固也。若是高明之创说。则于此不可不以朱子说参考而商量也。窃惟子思曰君子之道。费而隐。盖费言广也隐言微也。此理充满于宇宙之间。而为万事万物之道。无物不具。无处不有。至于事之至细。物之至微。不可分作两个者。而道无所不在。是故举全体而总言之则极于至大而无外。天下莫能载也。就其中而分言之则入于至小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0H 页
 而无间。天下莫能破焉。然其为理也。既无形像。又无声臭。有非见闻之所可及。其体可谓微矣。故曰君子之道。费而隐。然则以理之无处不在而言则曰费也。以理之不可见闻而言则曰隐也。故朱子以道之费者谓之形而上矣。道之为理。其不分明乎。朱子曰孔子其太极乎。今以太极明吾夫子一贯之道可乎。盖太极本无极也。是故动而生阳则为阳之太极。静而生阴则为阴之太极。阳变阴合。生水火金木土则为五行之太极。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则为四时之太极。在乾为乾之太极而乾道成男则为男之太极。在坤为坤之太极而坤道成女则为女之太极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为万物之太极。而万物各具一太极也。太极之道一以贯之者如此。夫子之心浑是太极之全体。故泛应曲当。无所处而非太极之理也。据此则所谓一贯之道。是理乎气乎。理与气兼者乎。朱子所谓理道二字。可互换者。亦可见道理之一般也。曾子圣门高弟也。盖有见于圣人之道。洋洋焉优优焉无处不在。而即事即物。一一理会。其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既皆讲明而体究之。至于许多疑文变节。无不讲究其洽好道理。以礼记曾子问一篇观之则可见
而无间。天下莫能破焉。然其为理也。既无形像。又无声臭。有非见闻之所可及。其体可谓微矣。故曰君子之道。费而隐。然则以理之无处不在而言则曰费也。以理之不可见闻而言则曰隐也。故朱子以道之费者谓之形而上矣。道之为理。其不分明乎。朱子曰孔子其太极乎。今以太极明吾夫子一贯之道可乎。盖太极本无极也。是故动而生阳则为阳之太极。静而生阴则为阴之太极。阳变阴合。生水火金木土则为五行之太极。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则为四时之太极。在乾为乾之太极而乾道成男则为男之太极。在坤为坤之太极而坤道成女则为女之太极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为万物之太极。而万物各具一太极也。太极之道一以贯之者如此。夫子之心浑是太极之全体。故泛应曲当。无所处而非太极之理也。据此则所谓一贯之道。是理乎气乎。理与气兼者乎。朱子所谓理道二字。可互换者。亦可见道理之一般也。曾子圣门高弟也。盖有见于圣人之道。洋洋焉优优焉无处不在。而即事即物。一一理会。其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既皆讲明而体究之。至于许多疑文变节。无不讲究其洽好道理。以礼记曾子问一篇观之则可见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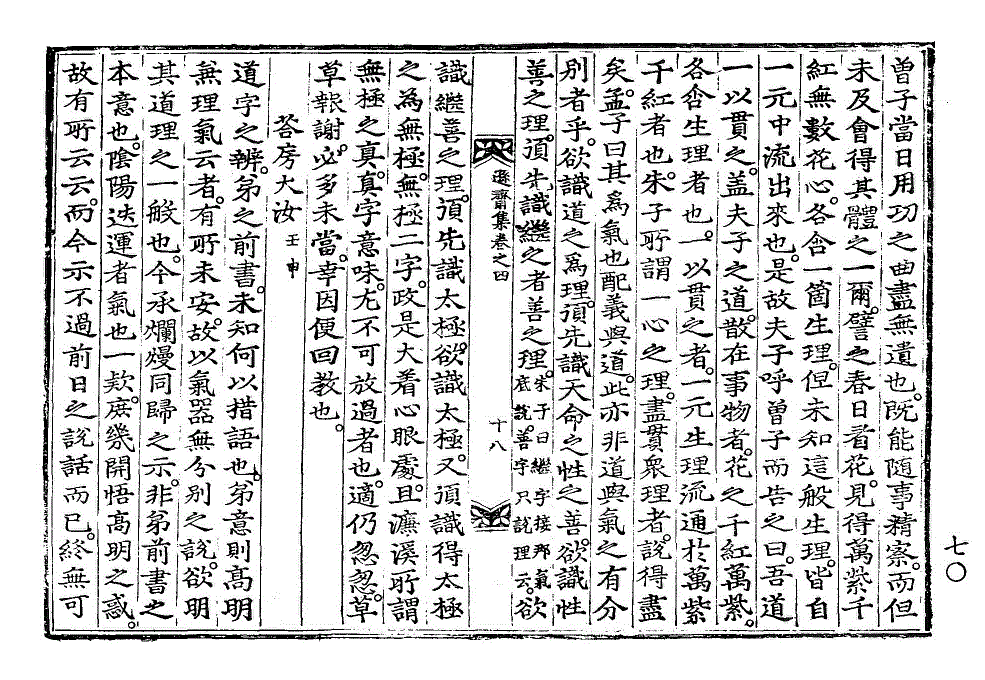 曾子当日用功之曲尽无遗也。既能随事精察。而但未及会得其体之一尔。譬之春日看花。见得万紫千红无数花心。各含一个生理。但未知这般生理。皆自一元中流出来也。是故夫子呼曾子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贯之。盖夫子之道。散在事物者。花之千红万紫。各含生理者也。一以贯之者。一元生理流通于万紫千红者也。朱子所谓一心之理。尽贯众理者。说得尽矣。孟子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此亦非道与气之有分别者乎。欲识道之为理。须先识天命之性之善。欲识性善之理。须先识继之者善之理。(朱子曰继字接那气底说。善字只说理云。)欲识继善之理。须先识太极。欲识太极。又须识得太极之为无极。无极二字。政是大着心眼处。且濂溪所谓无极之真。真字意味。尤不可放过者也。适仍匆匆。草草报谢。必多未当。幸因便回教也。
曾子当日用功之曲尽无遗也。既能随事精察。而但未及会得其体之一尔。譬之春日看花。见得万紫千红无数花心。各含一个生理。但未知这般生理。皆自一元中流出来也。是故夫子呼曾子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贯之。盖夫子之道。散在事物者。花之千红万紫。各含生理者也。一以贯之者。一元生理流通于万紫千红者也。朱子所谓一心之理。尽贯众理者。说得尽矣。孟子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此亦非道与气之有分别者乎。欲识道之为理。须先识天命之性之善。欲识性善之理。须先识继之者善之理。(朱子曰继字接那气底说。善字只说理云。)欲识继善之理。须先识太极。欲识太极。又须识得太极之为无极。无极二字。政是大着心眼处。且濂溪所谓无极之真。真字意味。尤不可放过者也。适仍匆匆。草草报谢。必多未当。幸因便回教也。答房大汝(壬申)
道字之辨。弟之前书。未知何以措语也。弟意则高明兼理气云者。有所未安。故以气器无分别之说。欲明其道理之一般也。今承烂熳同归之示。非弟前书之本意也。阴阳迭运者气也一款。庶几开悟高明之惑。故有所云云。而今示不过前日之说话而已。终无可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1H 页
 合之望。奈何奈何。然来书所谓道则气中主理而言云者。果是弟之说也。非弟之说。乃终古圣贤之说也。除却高明前后许多闲说话。只存此气中主理一句而已。则岂不洒然矣乎。更以此一句商量。则固知有烂熳之日耳。高明所谓道亦兼理气。器亦兼理气云者。恐失夫子本意也。一个形象之中。上者为道而下者为器。故明道先生曰截得上下最分明。若如高明之见。而道亦兼理气。器亦兼理气云尔。则何者为上而何者为下乎。先儒所谓道亦器器亦道云者。盖道者理也。器者气也。理无离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而理气二者元不相离之谓也。然理自理气自气。而一上一下。亦甚分明。非谓道亦兼理气。器亦兼理气。而上下之际。不分不明之谓也。试更思之如何。书曰道心惟微。盖道是性命之理。故心之循理而发出者道心也。于此可见道理之无分也。诗曰有物有则。则者如父子君臣之道也。朱子曰物者形也。则者理也。亦可见道理之无别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朱子曰阴阳气也。其理则道也。此非道理之一般者乎。孟子曰夫道一而已。若是兼理气而言者。则何可谓一而已乎。朱子答吕子约书曰。若如鄙意则道之得名。只是事物当然之
合之望。奈何奈何。然来书所谓道则气中主理而言云者。果是弟之说也。非弟之说。乃终古圣贤之说也。除却高明前后许多闲说话。只存此气中主理一句而已。则岂不洒然矣乎。更以此一句商量。则固知有烂熳之日耳。高明所谓道亦兼理气。器亦兼理气云者。恐失夫子本意也。一个形象之中。上者为道而下者为器。故明道先生曰截得上下最分明。若如高明之见。而道亦兼理气。器亦兼理气云尔。则何者为上而何者为下乎。先儒所谓道亦器器亦道云者。盖道者理也。器者气也。理无离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而理气二者元不相离之谓也。然理自理气自气。而一上一下。亦甚分明。非谓道亦兼理气。器亦兼理气。而上下之际。不分不明之谓也。试更思之如何。书曰道心惟微。盖道是性命之理。故心之循理而发出者道心也。于此可见道理之无分也。诗曰有物有则。则者如父子君臣之道也。朱子曰物者形也。则者理也。亦可见道理之无别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朱子曰阴阳气也。其理则道也。此非道理之一般者乎。孟子曰夫道一而已。若是兼理气而言者。则何可谓一而已乎。朱子答吕子约书曰。若如鄙意则道之得名。只是事物当然之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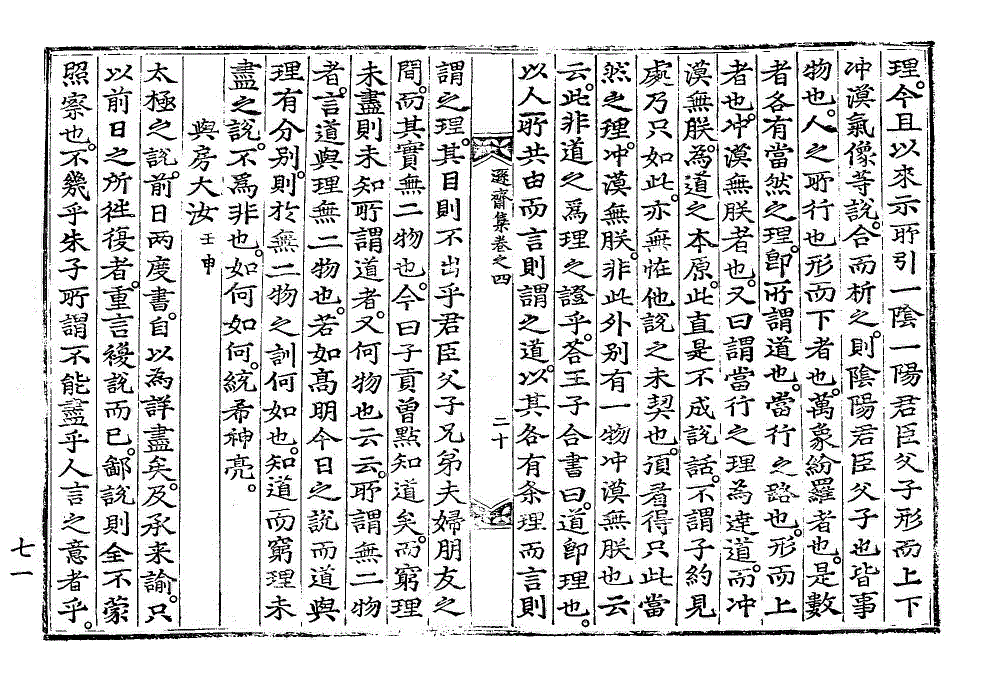 理。今且以来示所引一阴一阳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气像等说。合而析之。则阴阳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朕者也。又曰谓当行之理为达道。而冲漠无朕。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说话。不谓子约见处乃只如此。亦无怪他说之未契也。须看得只此当然之理。冲漠无朕。非此外别有一物冲漠无朕也云云。此非道之为理之證乎。答王子合书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其目则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其实无二物也。今曰子贡曾点知道矣。而穷理未尽则未知所谓道者。又何物也云云。所谓无二物者。言道与理无二物也。若如高明今日之说而道与理有分别。则于无二物之训何如也。知道而穷理未尽之说。不为非也。如何如何。统希神亮。
理。今且以来示所引一阴一阳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气像等说。合而析之。则阴阳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朕者也。又曰谓当行之理为达道。而冲漠无朕。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说话。不谓子约见处乃只如此。亦无怪他说之未契也。须看得只此当然之理。冲漠无朕。非此外别有一物冲漠无朕也云云。此非道之为理之證乎。答王子合书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其目则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其实无二物也。今曰子贡曾点知道矣。而穷理未尽则未知所谓道者。又何物也云云。所谓无二物者。言道与理无二物也。若如高明今日之说而道与理有分别。则于无二物之训何如也。知道而穷理未尽之说。不为非也。如何如何。统希神亮。与房大汝(壬申)
太极之说。前日两度书。自以为详尽矣。及承来谕。只以前日之所往复者。重言复说而已。鄙说则全不蒙照察也。不几乎朱子所谓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乎。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2H 页
 此非所望于高明者也。更取前书而详赐览观。则可知鄙说之未尝不同于高明之见也。请复得以详言之。盖太极之体。无大无小。不以天地而加大。不以一物而加小者。虽粗识理字者。皆知其如此矣。如愚者虽极昏迷。沉潜讲究。几年于玆。岂不知太极之体无大小哉。然则前日大小之说。其必有所以。而实非愚昧之创说也。濂溪先生曰是万为一。一实万分。此言太极之分而为万物之理。而合万物之理。为一太极也。朱子曰合以言之。万物统一体太极也。分以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此之谓也。以此观之则朱子固语大语小矣。朱子岂不知太极之体无大小。而引此语大小之说乎。大抵举天地万物而总言之则可谓之大也。就其中而各举一物之太极而言则可谓之小也。故朱子又有言曰一个大底包在。而中间自有细小之处。又曰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愚之大小之说。盖出于此。而岂谓太极之体。实有大者小者。如万物之有大小区别也哉。前日两书然字以上。推言朱子大小之说。然字以下分疏其太极之体。实无大小之义。而高明全不致察何耶。今以一尘言之则其为微。政所谓
此非所望于高明者也。更取前书而详赐览观。则可知鄙说之未尝不同于高明之见也。请复得以详言之。盖太极之体。无大无小。不以天地而加大。不以一物而加小者。虽粗识理字者。皆知其如此矣。如愚者虽极昏迷。沉潜讲究。几年于玆。岂不知太极之体无大小哉。然则前日大小之说。其必有所以。而实非愚昧之创说也。濂溪先生曰是万为一。一实万分。此言太极之分而为万物之理。而合万物之理。为一太极也。朱子曰合以言之。万物统一体太极也。分以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此之谓也。以此观之则朱子固语大语小矣。朱子岂不知太极之体无大小。而引此语大小之说乎。大抵举天地万物而总言之则可谓之大也。就其中而各举一物之太极而言则可谓之小也。故朱子又有言曰一个大底包在。而中间自有细小之处。又曰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愚之大小之说。盖出于此。而岂谓太极之体。实有大者小者。如万物之有大小区别也哉。前日两书然字以上。推言朱子大小之说。然字以下分疏其太极之体。实无大小之义。而高明全不致察何耶。今以一尘言之则其为微。政所谓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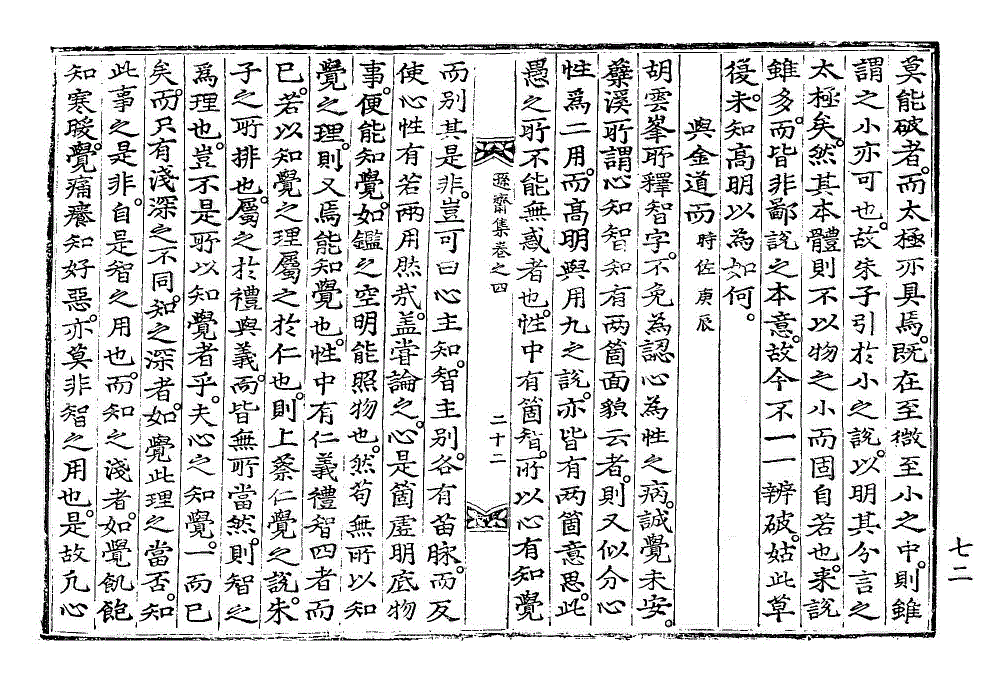 莫能破者。而太极亦具焉。既在至微至小之中。则虽谓之小亦可也。故朱子引于小之说。以明其分言之太极矣。然其本体则不以物之小而固自若也。来说虽多。而皆非鄙说之本意。故今不一一辨破。姑此草复。未知高明以为如何。
莫能破者。而太极亦具焉。既在至微至小之中。则虽谓之小亦可也。故朱子引于小之说。以明其分言之太极矣。然其本体则不以物之小而固自若也。来说虽多。而皆非鄙说之本意。故今不一一辨破。姑此草复。未知高明以为如何。与金道而(时佐○庚辰)
胡云峰所释智字。不免为认心为性之病。诚觉未安。檗溪所谓心知智知有两个面貌云者。则又似分心性为二用。而高明与用九之说。亦皆有两个意思。此愚之所不能无惑者也。性中有个智。所以心有知觉而别其是非。岂可曰心主知。智主别。各有苗脉。而反使心性有若两用然哉。盖尝论之。心是个虚明底物事。便能知觉。如鉴之空明能照物也。然苟无所以知觉之理。则又焉能知觉也。性中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若以知觉之理属之于仁也。则上蔡仁觉之说。朱子之所排也。属之于礼与义。而皆无所当然。则智之为理也。岂不是所以知觉者乎。夫心之知觉。一而已矣。而只有浅深之不同。知之深者。如觉此理之当否。知此事之是非。自是智之用也。而知之浅者。如觉饥饱知寒暖。觉痛痒知好恶。亦莫非智之用也。是故凡心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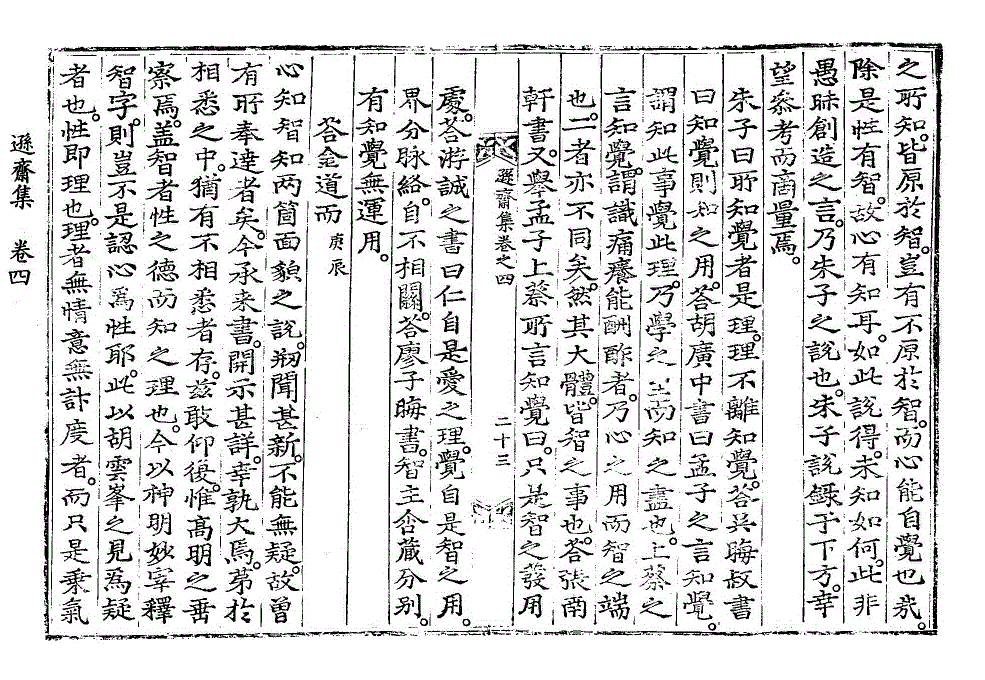 之所知。皆原于智。岂有不原于智。而心能自觉也哉。除是性有智。故心有知耳。如此说得。未知如何。此非愚昧创造之言。乃朱子之说也。朱子说录于下方。幸望参考而商量焉。
之所知。皆原于智。岂有不原于智。而心能自觉也哉。除是性有智。故心有知耳。如此说得。未知如何。此非愚昧创造之言。乃朱子之说也。朱子说录于下方。幸望参考而商量焉。朱子曰所知觉者是理。理不离知觉。答吴晦叔书曰知觉则知之用。答胡广中书曰孟子之言知觉。谓知此事觉此理。乃学之至而知之尽也。上蔡之言知觉。谓识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体。皆智之事也。答张南轩书。又举孟子上蔡所言知觉曰。只是智之发用处。答游诚之书曰仁自是爱之理。觉自是智之用。界分脉络。自不相关。答廖子晦书。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无运用。
答金道而(庚辰)
心知智知两个面貌之说。刱闻甚新。不能无疑。故曾有所奉达者矣。今承来书。开示甚详。幸孰大焉。第于相悉之中。犹有不相悉者存。玆敢仰复。惟高明之垂察焉。盖智者性之德而知之理也。今以神明妙宰释智字。则岂不是认心为性耶。此以胡云峰之见为疑者也。性即理也。理者无情意无计度者。而只是乘气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运用而已。是故朱子曰以智知者心也。今曰心知智知有两个面貌。则似涉于分心性为两用。故亦不能无惑于檗溪之言矣。来谕一端有可破惑者。其曰炳然者能照烛事物。而无判然者而别之则无所为准。不得为真知。判然者能分别是非。而无炳然者而照烛之则不能自运。无以成其知矣。此与鄙见不甚相远。而然两个面貌四字说得太重。恨未得奉质于檗溪案下也。遂庵书依教录呈耳。
运用而已。是故朱子曰以智知者心也。今曰心知智知有两个面貌。则似涉于分心性为两用。故亦不能无惑于檗溪之言矣。来谕一端有可破惑者。其曰炳然者能照烛事物。而无判然者而别之则无所为准。不得为真知。判然者能分别是非。而无炳然者而照烛之则不能自运。无以成其知矣。此与鄙见不甚相远。而然两个面貌四字说得太重。恨未得奉质于檗溪案下也。遂庵书依教录呈耳。与李慎夫(复三○戊午)
夫太极之理。无形体无造作者也。故实无离气而独立之时也。若与来说则太极之理。自能生活。悬空独立。而动然后阳乃生。静然后阴乃生。岂不大错乎。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者。非愚臆度刱造之见也。乃朱先生之训也。凡看文字。最宜活看。若或泥着则大失立言之本旨矣。朱先生所谓先有此理。其理已具等语。只是不杂乎气。而单言其理。以明枢纽根柢之本体也。岂如来谕之云乎。至于天地生灭之说。乃栗谷先生所言者。而亦本于朱先生之说也。此岂有可疑者也。一日可见一月之有晦朔。一月可见一岁之有春冬。一岁可见天地之有始终矣。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始矣。至若节斋之前后所论。亦本于朱先生之说。而平岩之所解一阳未动之时。谓之阴阳未生亦可云者。可谓详悉。细看其所谓截自一阳初动处之截字意味则果无疑矣。盖天地无穷生灭。故此天地未生之前。即前天地既灭之馀。而前天地前。又须有天地。推而上去。更无穷极。犹今日之子。根于昨日之亥。亥前有子。子前又有亥矣。故只是截断中间。此天地始辟之时。一阳初动处说起矣。一阳才动。宽阔光朗。天地定位。寒暑相推。则其所谓一阳未动之时。谓之阴阳未生云者。果有未莹者乎。若如来谕之所云。而一阳未动之时。谓之阳未生云尔。则此天地乃独阳而无阴也。其不可也必矣。盖详高明之意。以太极之理为先在上面。及其动后方生阳气。静后方生阴气。故立论如是。若是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奚可哉。揆诸道理。高明之见。终始未安。故复呈瞽说。幸回示其可否。
始矣。至若节斋之前后所论。亦本于朱先生之说。而平岩之所解一阳未动之时。谓之阴阳未生亦可云者。可谓详悉。细看其所谓截自一阳初动处之截字意味则果无疑矣。盖天地无穷生灭。故此天地未生之前。即前天地既灭之馀。而前天地前。又须有天地。推而上去。更无穷极。犹今日之子。根于昨日之亥。亥前有子。子前又有亥矣。故只是截断中间。此天地始辟之时。一阳初动处说起矣。一阳才动。宽阔光朗。天地定位。寒暑相推。则其所谓一阳未动之时。谓之阴阳未生云者。果有未莹者乎。若如来谕之所云。而一阳未动之时。谓之阳未生云尔。则此天地乃独阳而无阴也。其不可也必矣。盖详高明之意。以太极之理为先在上面。及其动后方生阳气。静后方生阴气。故立论如是。若是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奚可哉。揆诸道理。高明之见。终始未安。故复呈瞽说。幸回示其可否。与李慎夫(己未)
昨蒙枉顾。得两日之款。警诲之深。感发多矣。第太极阴阳之说。前此往复论辨。非至一再。而卒以鄙说为然。则自幸其所论之无异同矣。今又高明回头却步。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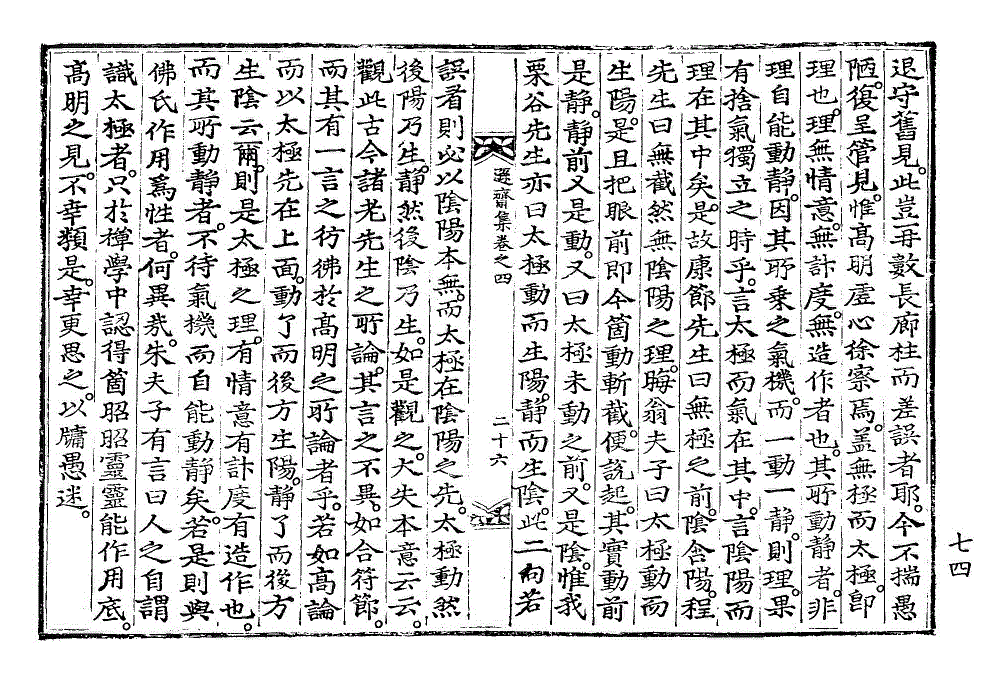 退守旧见。此岂再数长廊柱而差误者耶。今不揣愚陋。复呈管见。惟高明虚心徐察焉。盖无极而太极。即理也。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者也。其所动静者。非理自能动静。因其所乘之气机。而一动一静。则理。果有舍气独立之时乎。言太极而气在其中。言阴阳而理在其中矣。是故康节先生曰无极之前。阴含阳。程先生曰无截然无阴阳之理。晦翁夫子曰太极动而生阳。是且把眼前即今个动斩截。便说起。其实动前是静。静前又是动。又曰太极未动之前。又是阴。惟我栗谷先生亦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此二句若误看则必以阴阳本无。而太极在阴阳之先。太极动然后阳乃生。静然后阴乃生。如是观之。大失本意云云。观此古今诸老先生之所论。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而其有一言之彷佛于高明之所论者乎。若如高论而以太极先在上面。动了而后方生阳。静了而后方生阴云尔。则是太极之理。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也。而其所动静者。不待气机而自能动静矣。若是则与佛氏作用为性者。何异哉。朱夫子有言曰人之自谓识太极者。只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高明之见。不幸类是。幸更思之。以牗愚迷。
退守旧见。此岂再数长廊柱而差误者耶。今不揣愚陋。复呈管见。惟高明虚心徐察焉。盖无极而太极。即理也。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者也。其所动静者。非理自能动静。因其所乘之气机。而一动一静。则理。果有舍气独立之时乎。言太极而气在其中。言阴阳而理在其中矣。是故康节先生曰无极之前。阴含阳。程先生曰无截然无阴阳之理。晦翁夫子曰太极动而生阳。是且把眼前即今个动斩截。便说起。其实动前是静。静前又是动。又曰太极未动之前。又是阴。惟我栗谷先生亦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此二句若误看则必以阴阳本无。而太极在阴阳之先。太极动然后阳乃生。静然后阴乃生。如是观之。大失本意云云。观此古今诸老先生之所论。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而其有一言之彷佛于高明之所论者乎。若如高论而以太极先在上面。动了而后方生阳。静了而后方生阴云尔。则是太极之理。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也。而其所动静者。不待气机而自能动静矣。若是则与佛氏作用为性者。何异哉。朱夫子有言曰人之自谓识太极者。只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高明之见。不幸类是。幸更思之。以牗愚迷。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与李慎夫(庚申)
与李慎夫(庚申)所谕足见用意之深。甚慰甚慰。第其间有所未安者。故复呈瞽说。幸頫察焉。盖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虽是急于本而缓于末之意。然于此可见告子平日低看这气。而全不用功于气字上矣。故孟子以为未尽仅可。而开说其志。至气次而乃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于此亦可见此气之不可不养也。来谕念虑既失之后。何睱(一作暇)乎更求其气。此恐未然。以勿求于气。为未尽者。非谓瞬息介然之顷。求助于气。只言告子徒知力制不安之心。为不动之方。而不知更求于集义养气之间。而自然心不动尔。若曰心有不安。而即可求助于气而不动其心云尔。则恐无是理也。至于志壹则动气。此志字分明指不善者而言。何待朱子源头浊之训然后知其为不善也。只以孟子之说观之。已自皎然矣。气之壹者既是不善。则志之壹者何独不为之不善乎。夫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虽曰善事。而苟或专壹偏重则气便从之而躁暴矣。后段勿正之训。助长之戒。可以勘断也。若泛言志字则固有善恶矣。所谕志专在仁义则仁义之气动于外云者。亦似未稳。盖仁义根于心。因其端之发见而扩以充之。然后仁义粹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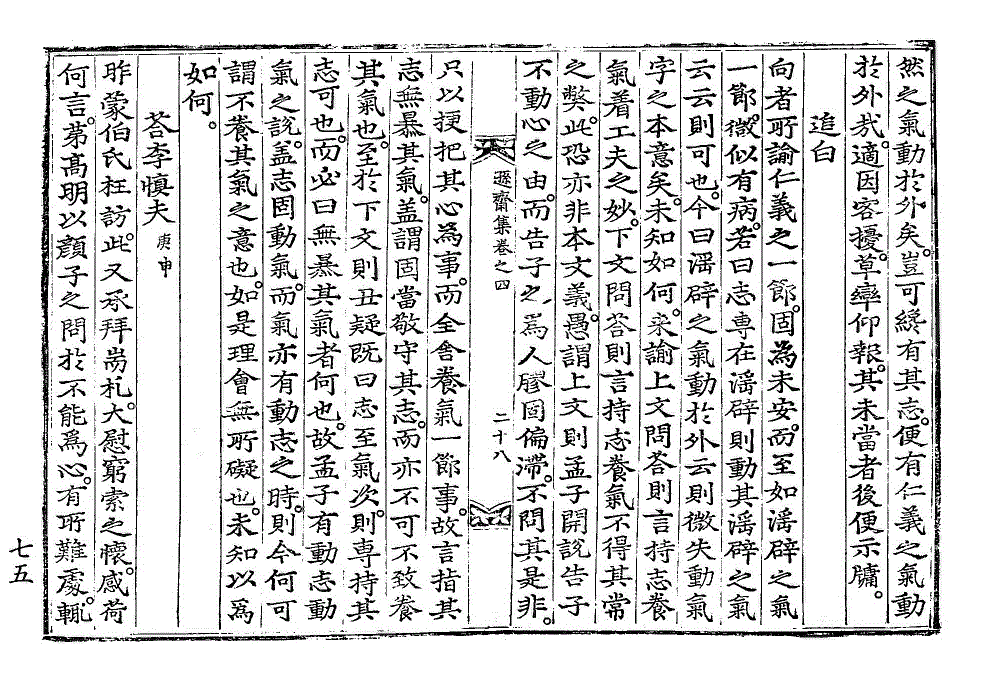 然之气动于外矣。岂可才有其志。便有仁义之气动于外哉。适因客扰。草率仰报。其未当者后便示牗。
然之气动于外矣。岂可才有其志。便有仁义之气动于外哉。适因客扰。草率仰报。其未当者后便示牗。追白
向者所谕仁义之一节。固为未安。而至如淫辟之气一节。微似有病。若曰志专在淫辟则动其淫辟之气云云则可也。今曰淫辟之气动于外云则微失动气字之本意矣。未知如何。来谕上文问答则言持志养气着工夫之妙。下文问答则言持志养气不得其常之弊。此恐亦非本文义。愚谓上文则孟子开说告子不动心之由。而告子之为人胶固偏滞。不问其是非。只以挭把其心为事。而全舍养气一节事。故言指其志无暴其气。盖谓固当敬守其志。而亦不可不致养其气也。至于下文则丑疑既曰志至气次。则专持其志可也。而必曰无暴其气者何也。故孟子有动志动气之说。盖志固动气。而气亦有动志之时。则今何可谓不养其气之意也。如是理会无所碍也。未知以为如何。
答李慎夫(庚申)
昨蒙伯氏枉访。此又承拜耑札。大慰穷索之怀。感荷何言。第高明以颜子之问于不能为心。有所难处。辄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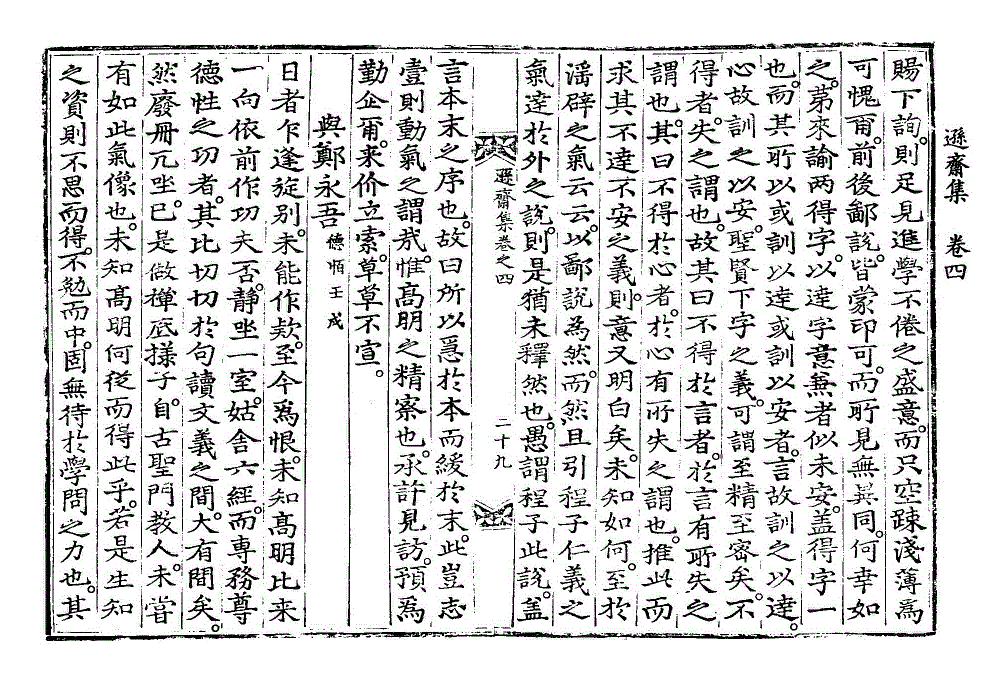 赐下询。则足见进学不倦之盛意。而只空疏浅薄为可愧尔。前后鄙说。皆蒙印可。而所见无异同。何幸如之。第来谕两得字。以达字意兼者似未安。盖得字一也。而其所以或训以达或训以安者。言故训之以达。心故训之以安。圣贤下字之义。可谓至精至密矣。不得者。失之谓也。故其曰不得于言者。于言有所失之谓也。其曰不得于心者。于心有所失之谓也。推此而求其不达不安之义。则意又明白矣。未知如何。至于淫辟之气云云。以鄙说为然。而然且引程子仁义之气达于外之说。则是犹未释然也。愚谓程子此说。盖言本末之序也。故曰所以急于本而缓于末。此岂志壹则动气之谓哉。惟高明之精察也。承许见访。预为勤企尔。来价立索。草草不宣。
赐下询。则足见进学不倦之盛意。而只空疏浅薄为可愧尔。前后鄙说。皆蒙印可。而所见无异同。何幸如之。第来谕两得字。以达字意兼者似未安。盖得字一也。而其所以或训以达或训以安者。言故训之以达。心故训之以安。圣贤下字之义。可谓至精至密矣。不得者。失之谓也。故其曰不得于言者。于言有所失之谓也。其曰不得于心者。于心有所失之谓也。推此而求其不达不安之义。则意又明白矣。未知如何。至于淫辟之气云云。以鄙说为然。而然且引程子仁义之气达于外之说。则是犹未释然也。愚谓程子此说。盖言本末之序也。故曰所以急于本而缓于末。此岂志壹则动气之谓哉。惟高明之精察也。承许见访。预为勤企尔。来价立索。草草不宣。与郑永吾(德恒○壬戌)
日者乍逢旋别。未能作款。至今为恨。未知高明比来一向依前作功夫否。静坐一室。姑舍六经。而专务尊德性之功者。其比切切于句读文义之间。大有间矣。然废册兀坐。已是做禅底㨾子。自古圣门教人。未尝有如此气像也。未知高明何从而得此乎。若是生知之资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固无待于学问之力也。其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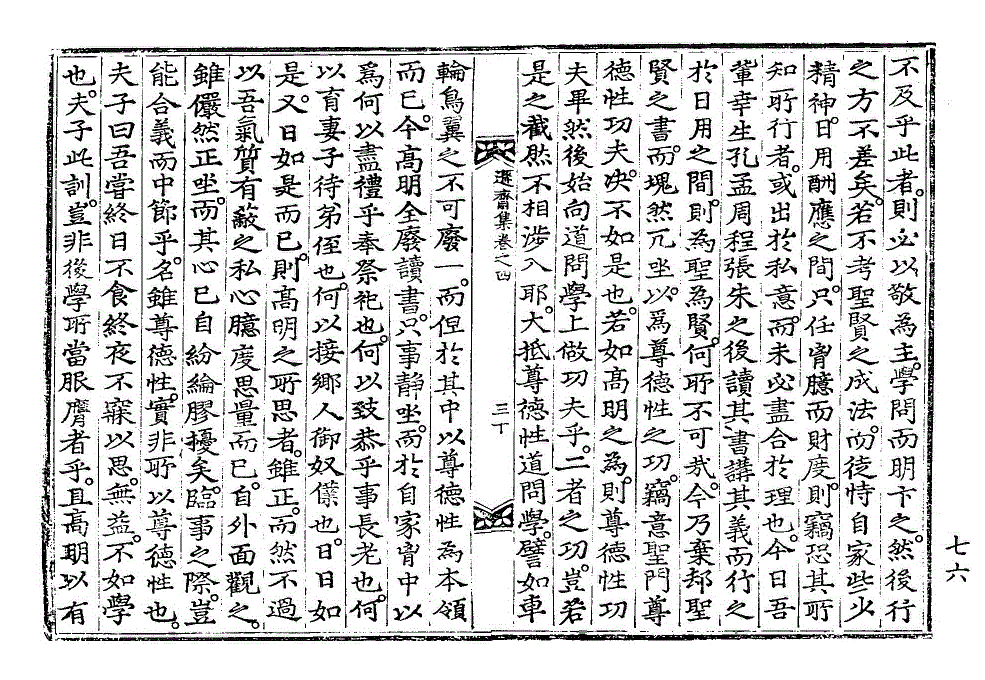 不及乎此者。则必以敬为主。学问而明卞之。然后行之方不差矣。若不考圣贤之成法。而徒恃自家些少精神。日用酬应之间。只任胸臆而财度。则窃恐其所知所行者。或出于私意。而未必尽合于理也。今日吾辈幸生孔孟周程张朱之后读其书讲其义而行之于日用之间。则为圣为贤。何所不可哉。今乃弃却圣贤之书。而块然兀坐。以为尊德性之功。窃意圣门尊德性功夫。决不如是也。若如高明之为。则尊德性功夫毕然后始向道问学上做功夫乎。二者之功。岂若是之截然不相涉入耶。大抵尊德性道问学。譬如车轮鸟翼之不可废一。而但于其中以尊德性为本领而已。今高明全废读书。只事静坐。而于自家胸中以为何以尽礼乎奉祭祀也。何以致恭乎事长老也。何以育妻子待弟侄也。何以接乡人御奴仆也。日日如是。又日如是而已。则高明之所思者。虽正。而然不过以吾气质有蔽之私心臆度思量而已。自外面观之。虽俨然正坐。而其心已自纷纶胶扰矣。临事之际。岂能合义而中节乎。名虽尊德性。实非所以尊德性也。夫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此训。岂非后学所当服膺者乎。且高明以有
不及乎此者。则必以敬为主。学问而明卞之。然后行之方不差矣。若不考圣贤之成法。而徒恃自家些少精神。日用酬应之间。只任胸臆而财度。则窃恐其所知所行者。或出于私意。而未必尽合于理也。今日吾辈幸生孔孟周程张朱之后读其书讲其义而行之于日用之间。则为圣为贤。何所不可哉。今乃弃却圣贤之书。而块然兀坐。以为尊德性之功。窃意圣门尊德性功夫。决不如是也。若如高明之为。则尊德性功夫毕然后始向道问学上做功夫乎。二者之功。岂若是之截然不相涉入耶。大抵尊德性道问学。譬如车轮鸟翼之不可废一。而但于其中以尊德性为本领而已。今高明全废读书。只事静坐。而于自家胸中以为何以尽礼乎奉祭祀也。何以致恭乎事长老也。何以育妻子待弟侄也。何以接乡人御奴仆也。日日如是。又日如是而已。则高明之所思者。虽正。而然不过以吾气质有蔽之私心臆度思量而已。自外面观之。虽俨然正坐。而其心已自纷纶胶扰矣。临事之际。岂能合义而中节乎。名虽尊德性。实非所以尊德性也。夫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此训。岂非后学所当服膺者乎。且高明以有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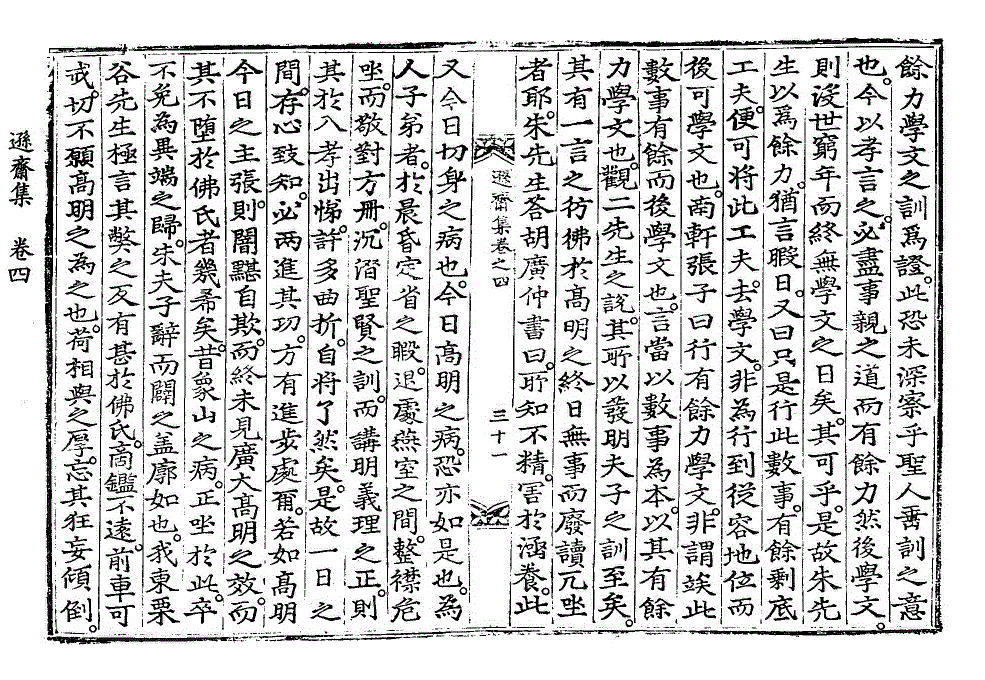 馀力学文之训为證。此恐未深察乎圣人垂训之意也。今以孝言之。必尽事亲之道而有馀力然后学文。则没世穷年而终无学文之日矣。其可乎。是故朱先生以为馀力。犹言暇日。又曰只是行此数事。有馀剩底工夫。便可将此工夫。去学文。非为行到从容地位而后可学文也。南轩张子曰行有馀力学文。非谓俟此数事有馀而后学文也。言当以数事为本。以其有馀力学文也。观二先生之说。其所以发明夫子之训至矣。其有一言之彷佛于高明之终日无事而废读兀坐者耶。朱先生答胡广仲书曰。所知不精。害于涵养。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今日高明之病。恐亦如是也。为人子弟者。于晨昏定省之睱(一作暇)。退处燕室之间。整襟危坐。而敬对方册。沉潜圣贤之训。而讲明义理之正。则其于入孝出悌。许多曲折。自将了然矣。是故一日之间。存心致知。必两进其功。方有进步处尔。若如高明今日之主张。则闇黮自欺。而终未见广大高明之效。而其不堕于佛氏者几希矣。昔象山之病。正坐于此。卒不免为异端之归。朱夫子辞而辟之盖廓如也。我东栗谷先生极言其弊之反有甚于佛氏。商鉴不远。前车可戒。切不愿高明之为之也。荷相与之厚。忘其狂妄倾倒。
馀力学文之训为證。此恐未深察乎圣人垂训之意也。今以孝言之。必尽事亲之道而有馀力然后学文。则没世穷年而终无学文之日矣。其可乎。是故朱先生以为馀力。犹言暇日。又曰只是行此数事。有馀剩底工夫。便可将此工夫。去学文。非为行到从容地位而后可学文也。南轩张子曰行有馀力学文。非谓俟此数事有馀而后学文也。言当以数事为本。以其有馀力学文也。观二先生之说。其所以发明夫子之训至矣。其有一言之彷佛于高明之终日无事而废读兀坐者耶。朱先生答胡广仲书曰。所知不精。害于涵养。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今日高明之病。恐亦如是也。为人子弟者。于晨昏定省之睱(一作暇)。退处燕室之间。整襟危坐。而敬对方册。沉潜圣贤之训。而讲明义理之正。则其于入孝出悌。许多曲折。自将了然矣。是故一日之间。存心致知。必两进其功。方有进步处尔。若如高明今日之主张。则闇黮自欺。而终未见广大高明之效。而其不堕于佛氏者几希矣。昔象山之病。正坐于此。卒不免为异端之归。朱夫子辞而辟之盖廓如也。我东栗谷先生极言其弊之反有甚于佛氏。商鉴不远。前车可戒。切不愿高明之为之也。荷相与之厚。忘其狂妄倾倒。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悚仄悚仄。未知高明以为如何。
悚仄悚仄。未知高明以为如何。与朴后老(松龄)
向者讲及论语井有人章。逝陷欺罔之义。而当时无书册可检看。未得明白分疏矣。更考本章旨义。则果无可疑者也。吾友所谓君子欺罔人云云者。大错此章之旨。不过曰人或欺君子曰井有人焉。则君子信之而往救。盖人落井中。非必无之理。故可使君子信而往救。此可逝可欺者也。人或罔君子而使之入井救人焉。则君子不之信而不入焉。盖入井救人。必无之理故也。此不可陷不可罔者也。大抵仁人君子明于理。故可以欺之以理。而不可罔之以无理也。然则所谓可逝不可陷者。盖曰可使君子往救。而不可使君子陷之井也。所谓可欺不可罔者。盖曰可以欺君子。而不可以罔君子也。夫子之训。分明如此。未知吾友以为如何。
答柳子宽(乘)
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一段。所论阳之用阴之体云者。大体则是矣。而所谓体虽成于天地之先。成字微似有病。改以具字则如何。平岩之以用起体立之体用。作妙用定体看者。固不是。盛论觑破其病。高见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精矣。熊物轩之说。亦未妥当。高明之以为牵合者得之。沙溪先生说至老先生说一段。所论看来。似欠浑全。盖阴阳之气所谓用也。而其质则体也。是以阴阳之气。起于天地之先。而其质立于天地之后。何以言之。阳之气始于天开之先。而其质立于天之圆。阴之气始于地辟之先。而其质立于地之方也。则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者可见也。两先生之所谓气为用质为体者。岂与妙用定体无分别乎。所谓妙用者。阳动阴静而循环不穷者是也。所谓定体者。分阴分阳而二气对待者是也。高明所谓与定体妙用之说无甚分别者。未知何如也。水之为物。随器而盈。火之为物。遇薪而燃。盈为静燃为动。静为体而动为用。故曰水体以器受。火用以薪传。然水之未入器时。必须流动。火之已上薪后。亦见其体。故曰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是故沙溪先生曰阴阳之用。起于天地未形之先。阴阳之体。立于天地已成之后。气为用质为体。老先生之说。亦不过如此矣。高见之以气属阳。以形属阴。而阳起阴立云者。大体则是矣。朱子曰天地变化。不为无阴。然物之未形。属乎阳。物正性命。不为无阳。然形气已定则属乎阴。朱子此训。与河图之生数
精矣。熊物轩之说。亦未妥当。高明之以为牵合者得之。沙溪先生说至老先生说一段。所论看来。似欠浑全。盖阴阳之气所谓用也。而其质则体也。是以阴阳之气。起于天地之先。而其质立于天地之后。何以言之。阳之气始于天开之先。而其质立于天之圆。阴之气始于地辟之先。而其质立于地之方也。则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者可见也。两先生之所谓气为用质为体者。岂与妙用定体无分别乎。所谓妙用者。阳动阴静而循环不穷者是也。所谓定体者。分阴分阳而二气对待者是也。高明所谓与定体妙用之说无甚分别者。未知何如也。水之为物。随器而盈。火之为物。遇薪而燃。盈为静燃为动。静为体而动为用。故曰水体以器受。火用以薪传。然水之未入器时。必须流动。火之已上薪后。亦见其体。故曰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是故沙溪先生曰阴阳之用。起于天地未形之先。阴阳之体。立于天地已成之后。气为用质为体。老先生之说。亦不过如此矣。高见之以气属阳。以形属阴。而阳起阴立云者。大体则是矣。朱子曰天地变化。不为无阴。然物之未形。属乎阳。物正性命。不为无阳。然形气已定则属乎阴。朱子此训。与河图之生数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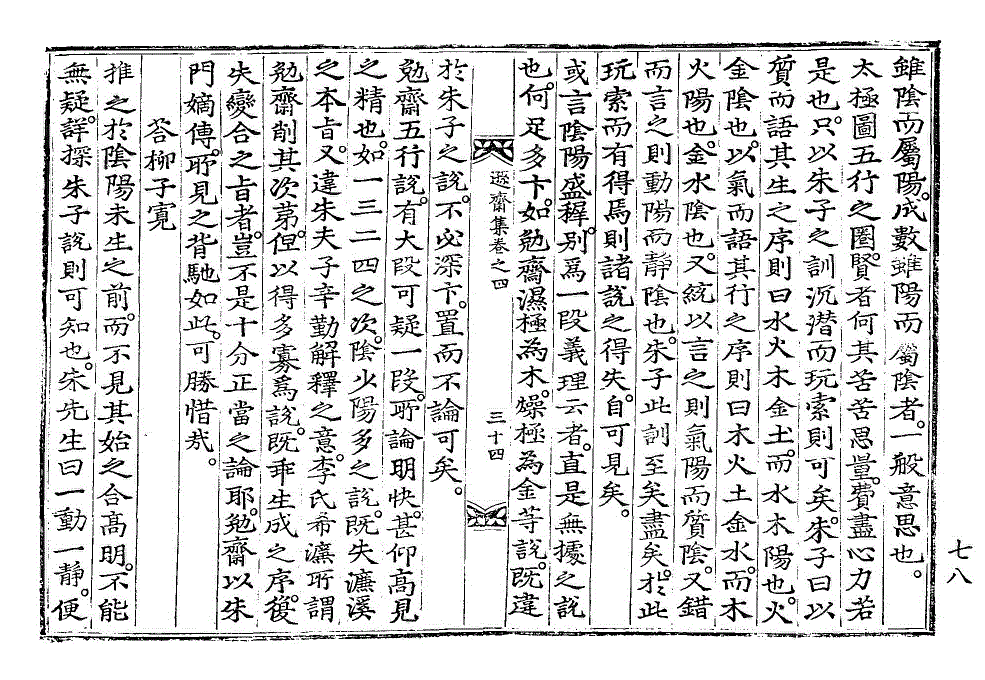 虽阴而属阳。成数虽阳而属阴者。一般意思也。
虽阴而属阳。成数虽阳而属阴者。一般意思也。太极图五行之圈。贤者何其苦苦思量。费尽心力若是也。只以朱子之训沉潜而玩索则可矣。朱子曰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以言之则气阳而质阴。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朱子此训至矣尽矣。于此玩索而有得焉则诸说之得失。自可见矣。
或言阴阳盛稚。别为一段义理云者。直是无据之说也。何足多卞。如勉斋湿极为木。燥极为金等说。既违于朱子之说。不必深卞。置而不论可矣。
勉斋五行说。有大段可疑一段。所论明快。甚仰高见之精也。如一三二四之次。阴少阳多之说。既失濂溪之本旨。又违朱夫子辛勤解释之意。李氏希濂所谓勉斋削其次第。但以得多寡为说。既乖生成之序。复失变合之旨者。岂不是十分正当之论耶。勉斋以朱门嫡传。所见之背驰如此。可胜惜哉。
答柳子宽
推之于阴阳未生之前。而不见其始之合高明。不能无疑。详探朱子说则可知也。朱先生曰一动一静。便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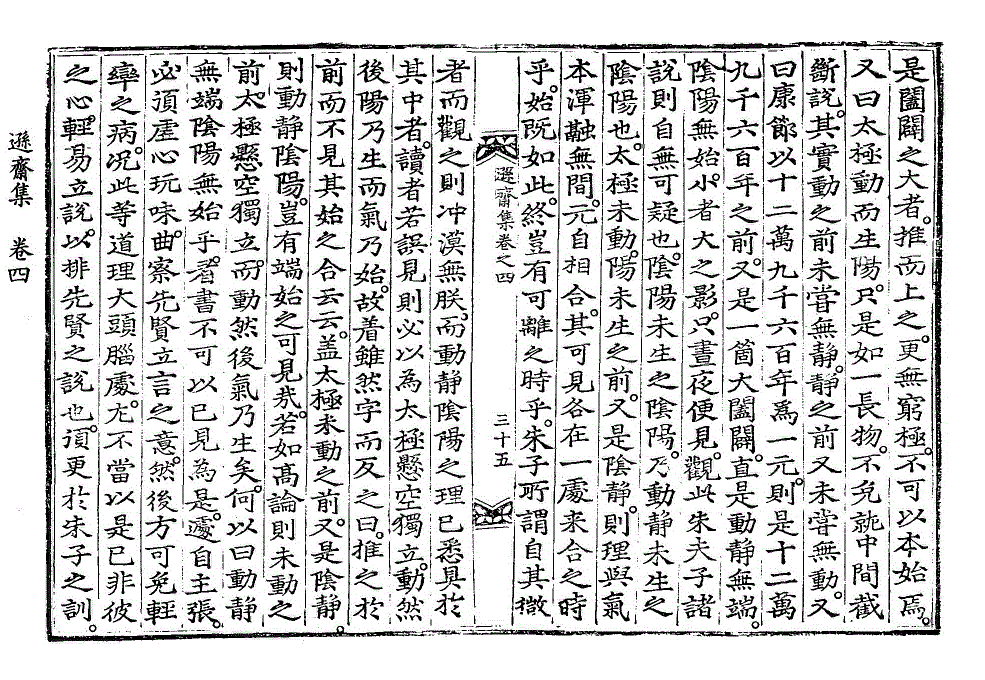 是阖辟之大者。推而上之。更无穷极。不可以本始焉。又曰太极动而生阳。只是如一长物。不免就中间截断说。其实动之前未尝无静。静之前又未尝无动。又曰康节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个大阖辟。直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小者大之影。只昼夜便见。观此朱夫子诸说则自无可疑也。阴阳未生之阴阳。乃动静未生之阴阳也。太极未动。阳未生之前。又是阴静。则理与气本浑融无间。元自相合。其可见各在一处来合之时乎。始既如此。终岂有可离之时乎。朱子所谓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者。读者若误见则必以为太极悬空独立。动然后阳乃生而气乃始。故着虽然字而反之曰。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云云。盖太极未动之前。又是阴静。则动静阴阳。岂有端始之可见哉。若如高论则未动之前。太极悬空独立。而动然后气乃生矣。何以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乎。看书不可以己见为是。遽自主张。必须虚心玩味。曲察先贤立言之意。然后方可免轻率之病。况此等道理大头脑处。尤不当以是己非彼之心。轻易立说。以排先贤之说也。须更于朱子之训。
是阖辟之大者。推而上之。更无穷极。不可以本始焉。又曰太极动而生阳。只是如一长物。不免就中间截断说。其实动之前未尝无静。静之前又未尝无动。又曰康节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个大阖辟。直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小者大之影。只昼夜便见。观此朱夫子诸说则自无可疑也。阴阳未生之阴阳。乃动静未生之阴阳也。太极未动。阳未生之前。又是阴静。则理与气本浑融无间。元自相合。其可见各在一处来合之时乎。始既如此。终岂有可离之时乎。朱子所谓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者。读者若误见则必以为太极悬空独立。动然后阳乃生而气乃始。故着虽然字而反之曰。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云云。盖太极未动之前。又是阴静。则动静阴阳。岂有端始之可见哉。若如高论则未动之前。太极悬空独立。而动然后气乃生矣。何以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乎。看书不可以己见为是。遽自主张。必须虚心玩味。曲察先贤立言之意。然后方可免轻率之病。况此等道理大头脑处。尤不当以是己非彼之心。轻易立说。以排先贤之说也。须更于朱子之训。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大着心眼而沉潜反覆如何。
大着心眼而沉潜反覆如何。答柳子宽
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此言无离合之可言也。解之曰그合(양을보지못고)그离(양을보지못다)云尔。若曰合(양을보지못다)则大错矣。大抵理与气。本混融无间。岂有离合之可见哉。此天地未生之前。即前天地既灭之馀。而乃太极未动之时也。太极乘着静机。而不是悬空独立底物事。则理与气元初混合。非如物之离而合合而离。而终始果无离合之可见。故云云乃尔。盛论胜于甲乙之见。而惟于合离二字之义有未明。故语多艰涩矣。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以五行生之之序言之。可谓精密矣。然孟子所谓仁义礼智。以性之体言。故其用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此所谓中正仁义。以心之动静言之。所谓中者动之极也。正者静之极也。仁则静极而复动者也。义则动极而复静者也。盖此心感动而蔼然恻怛者仁也。动而有节。无过不及者中也。中节而事裁物成则此心至此。休歇定叠。而又为制事之本。(论语义以为质注。朱子曰义者制事之本。)是则所谓义也。此心定叠而湛然虚静如明鉴止水。而至静之中。所以为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知觉者不昧。其真体亭亭当当。是则所谓正也。是知中仁为动。正义为静。静者为体而动者为用。故朱子曰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又曰主静者。主正与义也。又曰主静云者。以其相资之势言之。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如乾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则不能发散。龙蛇不蛰则无以奋。尺蠖不屈则无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据此则盛论之得失。可以勘断矣。贤者以中正明其发用之义。而愚以为言其动静之极也。
知觉者不昧。其真体亭亭当当。是则所谓正也。是知中仁为动。正义为静。静者为体而动者为用。故朱子曰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又曰主静者。主正与义也。又曰主静云者。以其相资之势言之。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如乾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则不能发散。龙蛇不蛰则无以奋。尺蠖不屈则无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据此则盛论之得失。可以勘断矣。贤者以中正明其发用之义。而愚以为言其动静之极也。答李馨徵(𦭎)
攻乎异端。异端如杨墨老佛之类也。以佛言之则人有陷于佛氏者。又有一人悯其陷于佛氏。辨其佛道之非。欲使归正。而倘非明于圣人之学而立其根本于吾道者。不可为矣。若于吾道。全无所见。未有正力。而专就异端。讲明其非。则其人亦或不免其反陷。故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者专治之义也。若曰为异端之学而有害云则甚无味。若曰攻伐异端云则亦非夫子之本意也。程子曰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焉入于其中。程子此训亦是吾道上无正力。而专就异端上讲其是非。欲使归正者。反陷于异端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之意也。人有放荡于淫声美色之中。而又有一人悯其放荡。不自量力。直入女乐丛中。言其淫声之不当听美色之不可近。欲使饰其身反于正。而其人苟无正心修身之正力。则渠亦骎骎然乐其淫声悦其美色。不自知其反陷于其中。其为害果如何也。攻乎异端之害亦如此也。集注所谓专治而欲精之则为害甚云者。岂非深得夫子之意欤。专治二字。正当玩味也。
之意也。人有放荡于淫声美色之中。而又有一人悯其放荡。不自量力。直入女乐丛中。言其淫声之不当听美色之不可近。欲使饰其身反于正。而其人苟无正心修身之正力。则渠亦骎骎然乐其淫声悦其美色。不自知其反陷于其中。其为害果如何也。攻乎异端之害亦如此也。集注所谓专治而欲精之则为害甚云者。岂非深得夫子之意欤。专治二字。正当玩味也。与舍弟(光元)
书中所示禽兽亦皆有仁义礼智之性云者。未知刱出于那边也。是据天命之性为说。而果似未然。子思所谓天命之性。是无论人与物。据其原头之理而言者也。若论其质则此理随气质而自为一性。譬之于水。水一也。而水贮十分清莹琉璃之器者。圣人之性也。水贮淡尘微昏之银器者。贤人之性也。水贮涂泥之磁器者。众人之性也。水渗在泥土之污处而元不见水体者。禽兽之性也。器之清浊。其品不同。而其中皆虚。故贮得这个水也。而惟彼泥土则塞而不虚。故无空水焉。盖吾人是禀得气之通者也。禽兽则禀得气之塞者也。是以人物之性绝不同。众人之性。比之则浊水也。而犹是贮于器之虚处而保其水体。如使
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久置静处。滓秽不动。则其本初之清。可得以见之矣。彼禽兽之性。比之则泥土。而其性不过为泞湿而已矣。大抵禽兽所禀之气。既是偏且塞。故其理亦偏塞。而如泥土之元无清净虚明之水体。则固不可名之以仁义礼智也。若使禽兽之气。不塞如人。则亦岂无仁义礼智之可名哉。是以虎狼之气至塞。而所禀之木气有一点通处。故有一点父子之仁。蜂蚁之气至塞。而所禀之金气有一段通处。故有一段君臣之义。其窒塞处元无仁义礼智之可名。盖理在气之通处。然后方为仁义礼智。而如水在器之虚处然后方为清净虚明。而理在气之塞处则不得为仁义礼智。如水在泥土则清净虚明不可名也。朱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岂物之所得而全。与夫殊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云者。岂不信哉。今曰禽兽仁义礼智之性。如泥中之明珠。则其粹然者人与物无异。何其与朱子说不同也。朱子尝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万代不易之正论也。是以朱子于中庸天命之性章句。言其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焉。于告子生之谓性集注。明其仁义礼智之人与物异焉。今若徒
久置静处。滓秽不动。则其本初之清。可得以见之矣。彼禽兽之性。比之则泥土。而其性不过为泞湿而已矣。大抵禽兽所禀之气。既是偏且塞。故其理亦偏塞。而如泥土之元无清净虚明之水体。则固不可名之以仁义礼智也。若使禽兽之气。不塞如人。则亦岂无仁义礼智之可名哉。是以虎狼之气至塞。而所禀之木气有一点通处。故有一点父子之仁。蜂蚁之气至塞。而所禀之金气有一段通处。故有一段君臣之义。其窒塞处元无仁义礼智之可名。盖理在气之通处。然后方为仁义礼智。而如水在器之虚处然后方为清净虚明。而理在气之塞处则不得为仁义礼智。如水在泥土则清净虚明不可名也。朱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岂物之所得而全。与夫殊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云者。岂不信哉。今曰禽兽仁义礼智之性。如泥中之明珠。则其粹然者人与物无异。何其与朱子说不同也。朱子尝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万代不易之正论也。是以朱子于中庸天命之性章句。言其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焉。于告子生之谓性集注。明其仁义礼智之人与物异焉。今若徒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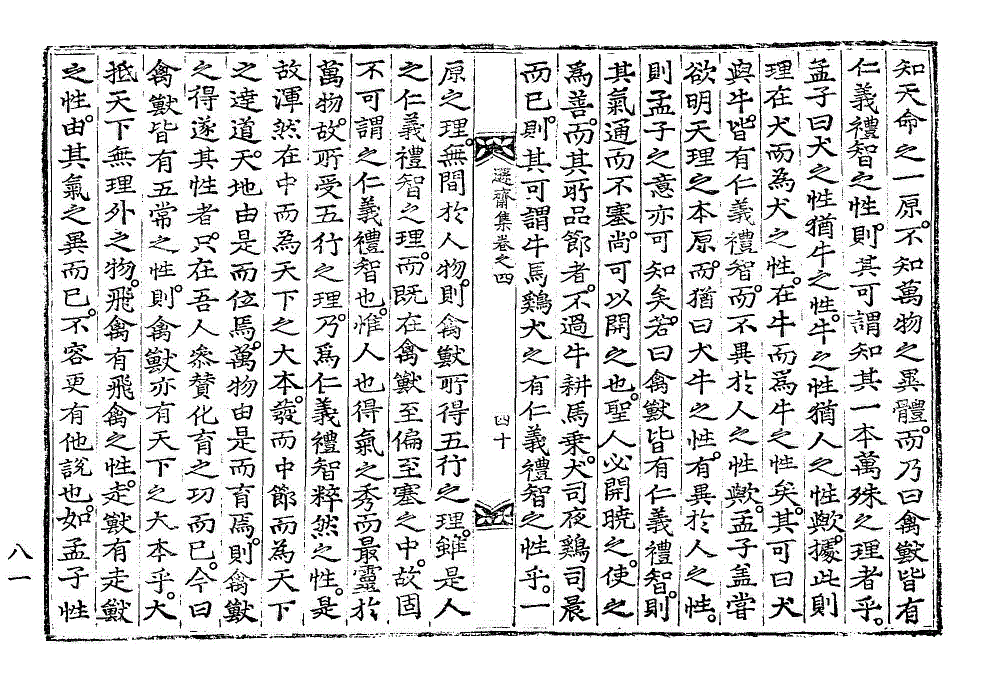 知天命之一原。不知万物之异体。而乃曰禽兽皆有仁义礼智之性。则其可谓知其一本万殊之理者乎。孟子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据此则理在犬而为犬之性。在牛而为牛之性矣。其可曰犬与牛。皆有仁义礼智。而不异于人之性欤。孟子盖尝欲明天理之本原。而犹曰犬牛之性。有异于人之性。则孟子之意亦可知矣。若曰禽兽皆有仁义礼智。则其气通而不塞。尚可以开之也。圣人必开晓之。使之为善。而其所品节者。不过牛耕马乘。犬司夜鸡司晨而已。则其可谓牛马鸡犬之有仁义礼智之性乎。一原之理。无间于人物。则禽兽所得五行之理。虽是人之仁义礼智之理。而既在禽兽至偏至塞之中。故固不可谓之仁义礼智也。惟人也得气之秀而最灵于万物。故所受五行之理。乃为仁义礼智粹然之性。是故浑然在中而为天下之大本。发而中节而为天下之达道。天地由是而位焉。万物由是而育焉。则禽兽之得遂其性者。只在吾人参赞化育之功而已。今曰禽兽皆有五常之性。则禽兽亦有天下之大本乎。大抵天下无理外之物。飞禽有飞禽之性。走兽有走兽之性。由其气之异而已。不容更有他说也。如孟子性
知天命之一原。不知万物之异体。而乃曰禽兽皆有仁义礼智之性。则其可谓知其一本万殊之理者乎。孟子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据此则理在犬而为犬之性。在牛而为牛之性矣。其可曰犬与牛。皆有仁义礼智。而不异于人之性欤。孟子盖尝欲明天理之本原。而犹曰犬牛之性。有异于人之性。则孟子之意亦可知矣。若曰禽兽皆有仁义礼智。则其气通而不塞。尚可以开之也。圣人必开晓之。使之为善。而其所品节者。不过牛耕马乘。犬司夜鸡司晨而已。则其可谓牛马鸡犬之有仁义礼智之性乎。一原之理。无间于人物。则禽兽所得五行之理。虽是人之仁义礼智之理。而既在禽兽至偏至塞之中。故固不可谓之仁义礼智也。惟人也得气之秀而最灵于万物。故所受五行之理。乃为仁义礼智粹然之性。是故浑然在中而为天下之大本。发而中节而为天下之达道。天地由是而位焉。万物由是而育焉。则禽兽之得遂其性者。只在吾人参赞化育之功而已。今曰禽兽皆有五常之性。则禽兽亦有天下之大本乎。大抵天下无理外之物。飞禽有飞禽之性。走兽有走兽之性。由其气之异而已。不容更有他说也。如孟子性逊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H 页
 善之论。则欲使人人明其善而复其初也。其所关系者甚大。而有功于万世矣。今之必欲明禽兽之有五常之性者。是亦不可已之论乎。不过为无益之空谈而已。今不必张皇辨斥。而汝亦骇然欲闻的确之论。故不能不如是开说焉。
善之论。则欲使人人明其善而复其初也。其所关系者甚大。而有功于万世矣。今之必欲明禽兽之有五常之性者。是亦不可已之论乎。不过为无益之空谈而已。今不必张皇辨斥。而汝亦骇然欲闻的确之论。故不能不如是开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