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x 页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杂著
杂著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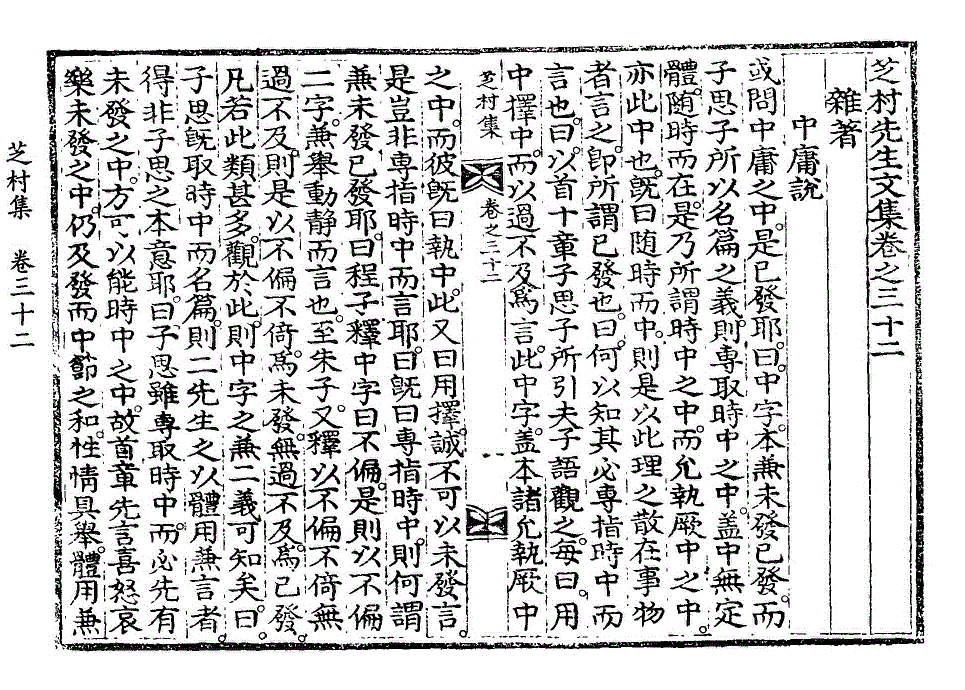 中庸说
中庸说或问中庸之中。是已发耶。曰。中字。本兼未发已发。而子思子所以名篇之义。则专取时中之中。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所谓时中之中。而允执厥中之中。亦此中也。既曰随时而中。则是以此理之散在事物者言之。即所谓已发也。曰。何以知其必专指时中而言也。曰。以首十章子思子所引夫子语观之。每曰。用中择中。而以过不及为言。此中字。盖本诸允执厥中之中。而彼既曰执中。此又曰用择。诚不可以未发言。是岂非专指时中而言耶。曰。既曰专指时中。则何谓兼未发已发耶。曰程子释中字曰不偏。是则以不偏二字。兼举动静而言也。至朱子。又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是以不偏不倚。为未发。无过不及。为已发。凡若此类甚多。观于此。则中字之兼二义可知矣。曰。子思既取时中而名篇。则二先生之以体用兼言者。得非子思之本意耶。曰。子思虽专取时中。而必先有未发之中。方可以能时中之中。故首章先言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仍及发而中节之和。性情具举。体用兼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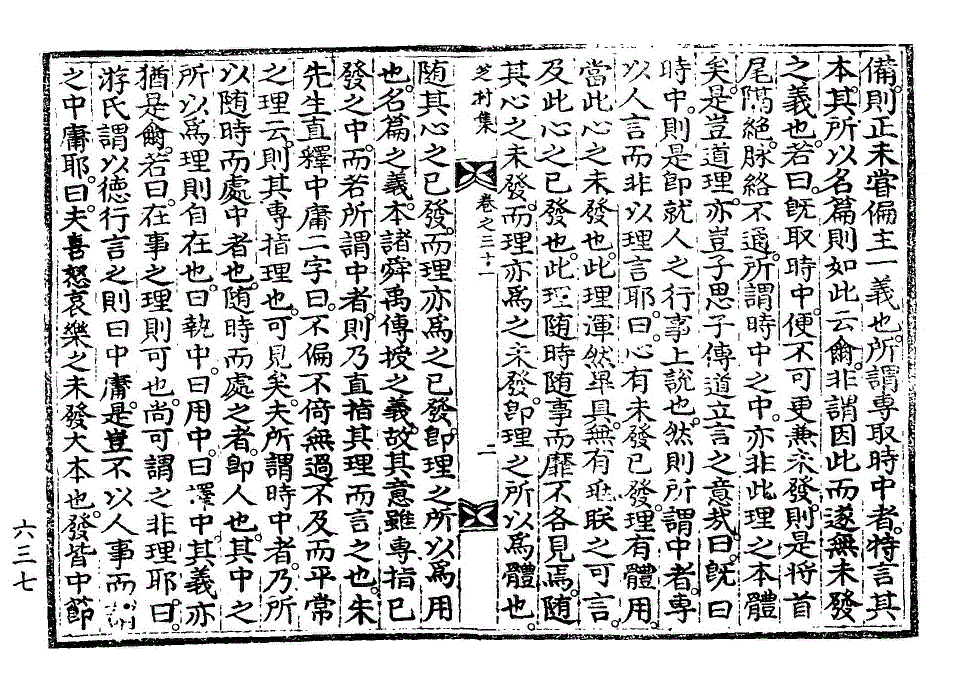 备。则正未尝偏主一义也。所谓专取时中者。特言其本。其所以名篇则如此云尔。非谓因此而遂无未发之义也。若曰。既取时中。便不可更兼未发。则是将首尾隔绝。脉络不通。所谓时中之中。亦非此理之本体矣。是岂道理。亦岂子思子传道立言之意哉。曰。既曰时中。则是即就人之行事上说也。然则所谓中者。专以人言而非以理言耶。曰。心有未发已发。理有体用。当此心之未发也。此理浑然毕具。无有兆眹之可言。及此心之已发也。此理随时随事而靡不各见焉。随其心之未发。而理亦为之未发。即理之所以为体也。随其心之已发。而理亦为之已发。即理之所以为用也。名篇之义。本诸舜禹传授之义。故其意虽专指已发之中。而若所谓中者。则乃直指其理而言之也。朱先生直释中庸二字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云。则其专指理也。可见矣。夫所谓时中者。乃所以随时而处中者也。随时而处之者。即人也。其中之所以为理则自在也。曰执中。曰用中。曰择中。其义亦犹是尔。若曰。在事之理则可也。尚可谓之非理耶。曰。游氏谓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岂不以人事而谓之中庸耶。曰。夫喜怒哀乐之未发大本也。发皆中节
备。则正未尝偏主一义也。所谓专取时中者。特言其本。其所以名篇则如此云尔。非谓因此而遂无未发之义也。若曰。既取时中。便不可更兼未发。则是将首尾隔绝。脉络不通。所谓时中之中。亦非此理之本体矣。是岂道理。亦岂子思子传道立言之意哉。曰。既曰时中。则是即就人之行事上说也。然则所谓中者。专以人言而非以理言耶。曰。心有未发已发。理有体用。当此心之未发也。此理浑然毕具。无有兆眹之可言。及此心之已发也。此理随时随事而靡不各见焉。随其心之未发。而理亦为之未发。即理之所以为体也。随其心之已发。而理亦为之已发。即理之所以为用也。名篇之义。本诸舜禹传授之义。故其意虽专指已发之中。而若所谓中者。则乃直指其理而言之也。朱先生直释中庸二字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云。则其专指理也。可见矣。夫所谓时中者。乃所以随时而处中者也。随时而处之者。即人也。其中之所以为理则自在也。曰执中。曰用中。曰择中。其义亦犹是尔。若曰。在事之理则可也。尚可谓之非理耶。曰。游氏谓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岂不以人事而谓之中庸耶。曰。夫喜怒哀乐之未发大本也。发皆中节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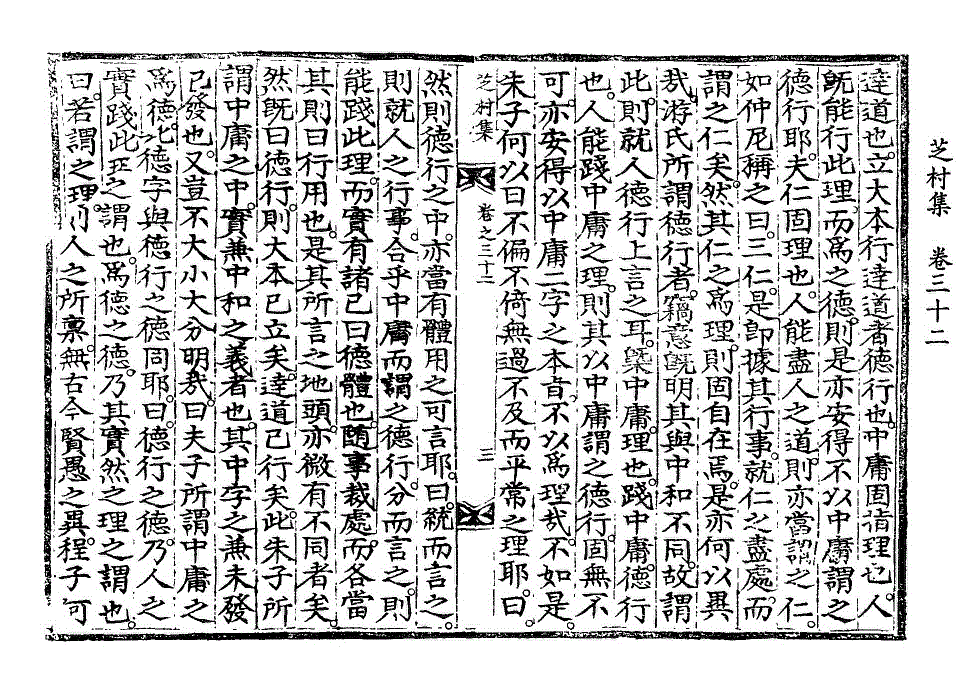 达道也。立大本行达道者德行也。中庸固指理也。人既能行此理。而为之德。则是亦安得不以中庸谓之德行耶。夫仁固理也。人能尽人之道。则亦当谓之仁。如仲尼称之曰。三仁。是即据其行事。就仁之尽处。而谓之仁矣。然其仁之为理。则固自在焉。是亦何以异哉。游氏所谓德行者。窃意既明其与中和不同。故谓此。则就人德行上言之耳。槩中庸。理也。践中庸。德行也。人能践中庸之理。则其以中庸谓之德行。固无不可。亦安得以中庸二字之本旨。不以为理哉。不如是。朱子何以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耶。曰。然则德行之中。亦当有体用之可言耶。曰。统而言之。则就人之行事。合乎中庸而谓之德行。分而言之。则能践此理。而实有诸己曰德体也。随事裁处。而各当其则曰行用也。是其所言之地头。亦微有不同者矣。然既曰德行。则大本已立矣。达道已行矣。此朱子所谓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者也。其中字之兼未发已发也。又岂不大小大分明哉。曰夫子所谓中庸之为德。此德字与德行之德同耶。曰。德行之德。乃人之实践此理之谓也。为德之德。乃其实然之理之谓也。曰。若谓之理。则人之所禀。无古今贤愚之异。程子何
达道也。立大本行达道者德行也。中庸固指理也。人既能行此理。而为之德。则是亦安得不以中庸谓之德行耶。夫仁固理也。人能尽人之道。则亦当谓之仁。如仲尼称之曰。三仁。是即据其行事。就仁之尽处。而谓之仁矣。然其仁之为理。则固自在焉。是亦何以异哉。游氏所谓德行者。窃意既明其与中和不同。故谓此。则就人德行上言之耳。槩中庸。理也。践中庸。德行也。人能践中庸之理。则其以中庸谓之德行。固无不可。亦安得以中庸二字之本旨。不以为理哉。不如是。朱子何以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耶。曰。然则德行之中。亦当有体用之可言耶。曰。统而言之。则就人之行事。合乎中庸而谓之德行。分而言之。则能践此理。而实有诸己曰德体也。随事裁处。而各当其则曰行用也。是其所言之地头。亦微有不同者矣。然既曰德行。则大本已立矣。达道已行矣。此朱子所谓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者也。其中字之兼未发已发也。又岂不大小大分明哉。曰夫子所谓中庸之为德。此德字与德行之德同耶。曰。德行之德。乃人之实践此理之谓也。为德之德。乃其实然之理之谓也。曰。若谓之理。则人之所禀。无古今贤愚之异。程子何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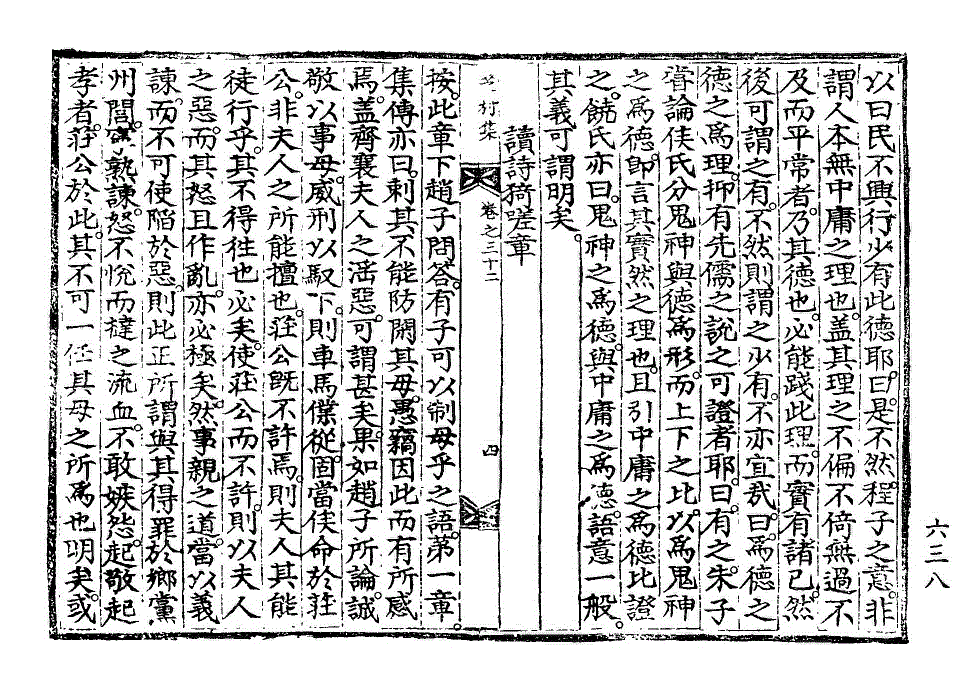 以曰民不兴行少有此德耶。曰。是不然。程子之意。非谓人本无中庸之理也。盖其理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者。乃其德也。必能践此理。而实有诸己。然后可谓之有。不然则谓之少有。不亦宜哉。曰。为德之德之为理。抑有先儒之说之可證者耶。曰。有之。朱子尝论侯氏分鬼神与德为形。而上下之比。以为鬼神之为德。即言其实然之理也。且引中庸之为德比證之。饶氏亦曰。鬼神之为德。与中庸之为德。语意一般。其义可谓明矣。
以曰民不兴行少有此德耶。曰。是不然。程子之意。非谓人本无中庸之理也。盖其理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者。乃其德也。必能践此理。而实有诸己。然后可谓之有。不然则谓之少有。不亦宜哉。曰。为德之德之为理。抑有先儒之说之可證者耶。曰。有之。朱子尝论侯氏分鬼神与德为形。而上下之比。以为鬼神之为德。即言其实然之理也。且引中庸之为德比證之。饶氏亦曰。鬼神之为德。与中庸之为德。语意一般。其义可谓明矣。读诗猗嗟章
按。此章下赵子问答。有子可以制母乎之语。第一章。集传亦曰。刺其不能防闲其母。愚窃因此而有所感焉。盖齐襄夫人之淫恶。可谓甚矣。果如赵子所论。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则车马仆从。固当俟命于庄公。非夫人之所能擅也。庄公既不许焉。则夫人其能徒行乎。其不得往也必矣。使庄公而不许。则以夫人之恶。而其怒且作乱。亦必极矣。然事亲之道。当以义谏。而不可使陷于恶。则此正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嫉怨。起敬起孝者。庄公于此。其不可一任其母之所为也明矣。或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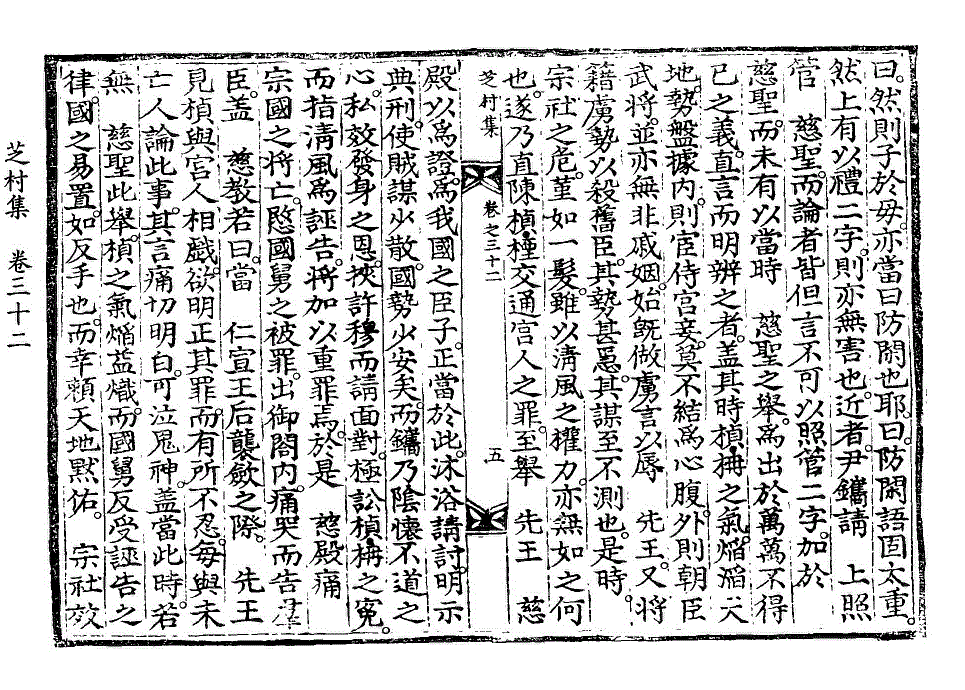 曰。然则子于母。亦当曰防闲也耶。曰。防闲语固太重。然上有以礼二字。则亦无害也。近者。尹鑴请 上照管 慈圣。而论者皆但言不可以照管二字。加于 慈圣。而未有以当时 慈圣之举。为出于万万不得已之义。直言而明辨之者。盖其时桢,楠之气。焰滔天地。势盘据内。则宦侍宫妾。莫不结为心腹。外则朝臣武将。并亦无非戚姻。始既做虏言以辱 先王。又将籍虏势以杀旧臣。其势甚急。其谋至不测也。是时。 宗社之危。堇如一发。虽以清风之权力。亦无如之何也。遂乃直陈桢,㮒交通宫人之罪。至举 先王 慈殿以为證。为我国之臣子。正当于此。沐浴请讨。明示典刑。使贼谋少散。国势少安矣。而鑴乃阴怀不道之心。私效发身之恩。挟许穆而请面对。极讼桢,楠之冤。而指清风为诬告。将加以重罪焉。于是 慈殿痛 宗国之将亡。悯国舅之被罪。出御閤内。痛哭而告群臣。盖 慈教若曰。当 仁宣王后袭敛之际。 先王见桢与宫人相戏。欲明正其罪。而有所不忍。每与未亡人论此事。其言痛切明白。可泣鬼神。盖当此时。若无 慈圣此举。桢之气焰益炽。而国舅反受诬告之律。国之易置。如反手也。而幸赖天地默佑。 宗社效
曰。然则子于母。亦当曰防闲也耶。曰。防闲语固太重。然上有以礼二字。则亦无害也。近者。尹鑴请 上照管 慈圣。而论者皆但言不可以照管二字。加于 慈圣。而未有以当时 慈圣之举。为出于万万不得已之义。直言而明辨之者。盖其时桢,楠之气。焰滔天地。势盘据内。则宦侍宫妾。莫不结为心腹。外则朝臣武将。并亦无非戚姻。始既做虏言以辱 先王。又将籍虏势以杀旧臣。其势甚急。其谋至不测也。是时。 宗社之危。堇如一发。虽以清风之权力。亦无如之何也。遂乃直陈桢,㮒交通宫人之罪。至举 先王 慈殿以为證。为我国之臣子。正当于此。沐浴请讨。明示典刑。使贼谋少散。国势少安矣。而鑴乃阴怀不道之心。私效发身之恩。挟许穆而请面对。极讼桢,楠之冤。而指清风为诬告。将加以重罪焉。于是 慈殿痛 宗国之将亡。悯国舅之被罪。出御閤内。痛哭而告群臣。盖 慈教若曰。当 仁宣王后袭敛之际。 先王见桢与宫人相戏。欲明正其罪。而有所不忍。每与未亡人论此事。其言痛切明白。可泣鬼神。盖当此时。若无 慈圣此举。桢之气焰益炽。而国舅反受诬告之律。国之易置。如反手也。而幸赖天地默佑。 宗社效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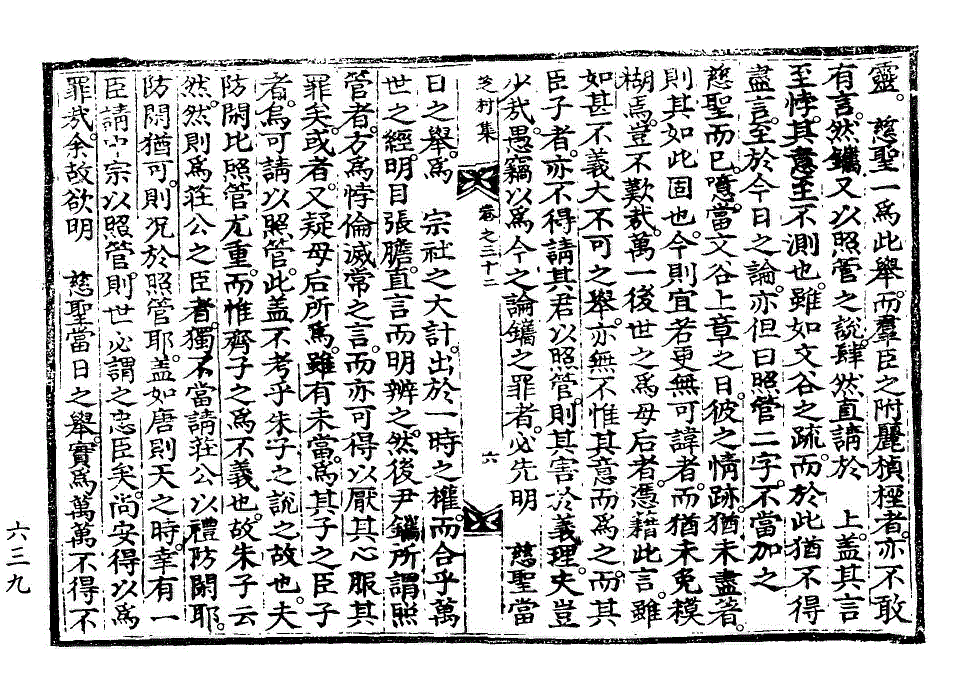 灵。 慈圣一为此举。而群臣之附丽桢㮒者。亦不敢有言。然鑴又以照管之说。肆然直请于 上。盖其言至悖。其意至不测也。虽如文谷之疏。而于此犹不得尽言。至于今日之论。亦但曰照管二字。不当加之 慈圣而已。噫。当文谷上章之日。彼之情迹。犹未尽著。则其如此固也。今则宜若更无可讳者。而犹未免模糊焉。岂不叹哉。万一后世之为母后者。凭藉此言。虽如甚不义大不可之举。亦无不惟其意而为之。而其臣子者。亦不得请其君以照管。则其害于义理。夫岂少哉。愚窃以为今之论鑴之罪者。必先明 慈圣当日之举。为 宗社之大计。出于一时之权。而合乎万世之经。明目张胆。直言而明辨之。然后尹鑴所谓照管者。方为悖伦灭常之言。而亦可得以厌其心服其罪矣。或者。又疑母后所为。虽有未当。为其子之臣子者。乌可请以照管。此盖不考乎朱子之说之故也。夫防闲比照管尤重。而惟齐子之为不义也。故朱子云然。然则为庄公之臣者。独不当请庄公以礼防闲耶。防闲犹可。则况于照管耶。盖如唐则天之时。幸有一臣请中宗以照管。则世必谓之忠臣矣。尚安得以为罪哉。余故欲明 慈圣当日之举。实为万万不得不
灵。 慈圣一为此举。而群臣之附丽桢㮒者。亦不敢有言。然鑴又以照管之说。肆然直请于 上。盖其言至悖。其意至不测也。虽如文谷之疏。而于此犹不得尽言。至于今日之论。亦但曰照管二字。不当加之 慈圣而已。噫。当文谷上章之日。彼之情迹。犹未尽著。则其如此固也。今则宜若更无可讳者。而犹未免模糊焉。岂不叹哉。万一后世之为母后者。凭藉此言。虽如甚不义大不可之举。亦无不惟其意而为之。而其臣子者。亦不得请其君以照管。则其害于义理。夫岂少哉。愚窃以为今之论鑴之罪者。必先明 慈圣当日之举。为 宗社之大计。出于一时之权。而合乎万世之经。明目张胆。直言而明辨之。然后尹鑴所谓照管者。方为悖伦灭常之言。而亦可得以厌其心服其罪矣。或者。又疑母后所为。虽有未当。为其子之臣子者。乌可请以照管。此盖不考乎朱子之说之故也。夫防闲比照管尤重。而惟齐子之为不义也。故朱子云然。然则为庄公之臣者。独不当请庄公以礼防闲耶。防闲犹可。则况于照管耶。盖如唐则天之时。幸有一臣请中宗以照管。则世必谓之忠臣矣。尚安得以为罪哉。余故欲明 慈圣当日之举。实为万万不得不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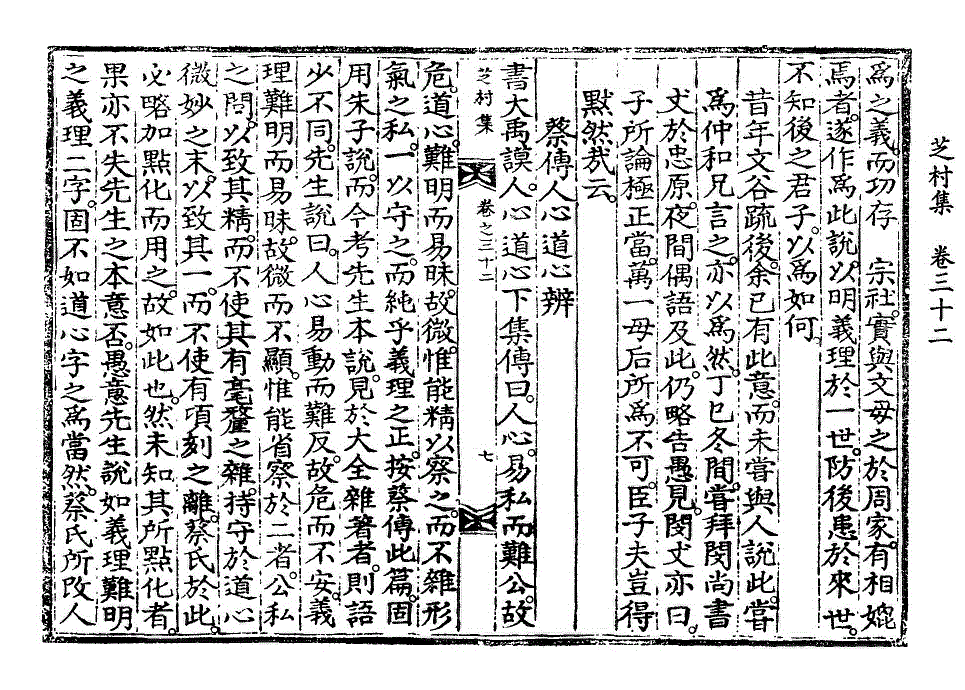 为之义。而功存 宗社。实与文母之于周家。有相媲焉者。遂作为此说。以明义理于一世。防后患于来世。不知后之君子。以为如何。
为之义。而功存 宗社。实与文母之于周家。有相媲焉者。遂作为此说。以明义理于一世。防后患于来世。不知后之君子。以为如何。昔年文谷疏后。余已有此意。而未尝与人说此。尝为仲和兄言之。亦以为然。丁巳冬间。尝拜闵尚书丈于忠原。夜间偶语及此。仍略告愚见。闵丈亦曰。子所论极正当。万一母后所为不可。臣子夫岂得默然哉云。
蔡传人心道心辨
书大禹谟。人心道心下集传曰。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按蔡传此篇。固用朱子说。而今考先生本说。见于大全杂著者。则语少不同。先生说曰。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问。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杂。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末。以致其一。而不使有顷刻之离。蔡氏于此。必略加点化而用之。故如此也。然未知其所点化者。果亦不失先生之本意否。愚意先生说如义理难明之义理二字。固不如道心字之为当然。蔡氏所改人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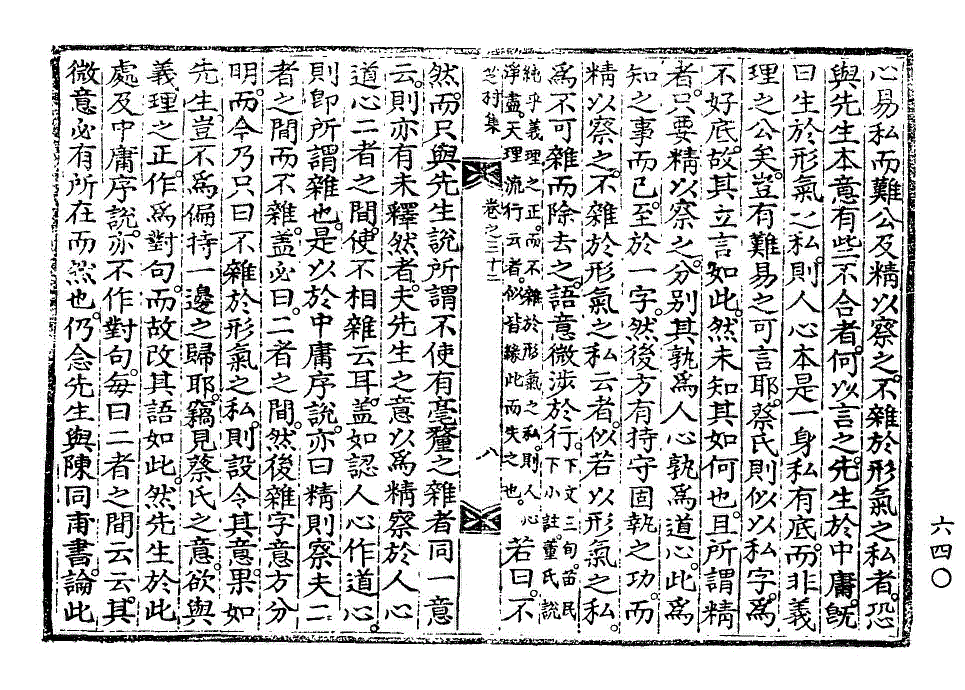 心易私而难公及精以察之。不杂于形气之私者。恐与先生本意有些不合者。何以言之。先生于中庸。既曰生于形气之私。则人心本是一身私有底。而非义理之公矣。岂有难易之可言耶。蔡氏则似以私字。为不好底。故其立言如此。然未知其如何也。且所谓精者。只要精以察之。分别其孰为人心孰为道心。此为知之事而已。至于一字。然后方有持守固执之功。而精以察之。不杂于形气之私云者。似若以形气之私。为不可杂而除去之。语意微涉于行。(下文三旬。苗民下小注。董氏说纯乎义理之正。而不杂于形气之私。则人心净尽。天理流行云者。似皆缘此而失之也。)若曰。不然。而只与先生说所谓不使有毫釐之杂者同一意云。则亦有未释然者。夫先生之意以为精察于人心道心二者之间。使不相杂云耳。盖如认人心作道心。则即所谓杂也。是以于中庸序说。亦曰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盖必曰。二者之间。然后杂字意方分明。而今乃只曰不杂于形气之私。则设令其意。果如先生。岂不为偏持一边之归耶。窃见蔡氏之意。欲与义理之正。作为对句。而故改其语如此。然先生于此处及中庸序说。亦不作对句。每曰二者之间云云。其微意必有所在而然也。仍念先生与陈同甫书。论此
心易私而难公及精以察之。不杂于形气之私者。恐与先生本意有些不合者。何以言之。先生于中庸。既曰生于形气之私。则人心本是一身私有底。而非义理之公矣。岂有难易之可言耶。蔡氏则似以私字。为不好底。故其立言如此。然未知其如何也。且所谓精者。只要精以察之。分别其孰为人心孰为道心。此为知之事而已。至于一字。然后方有持守固执之功。而精以察之。不杂于形气之私云者。似若以形气之私。为不可杂而除去之。语意微涉于行。(下文三旬。苗民下小注。董氏说纯乎义理之正。而不杂于形气之私。则人心净尽。天理流行云者。似皆缘此而失之也。)若曰。不然。而只与先生说所谓不使有毫釐之杂者同一意云。则亦有未释然者。夫先生之意以为精察于人心道心二者之间。使不相杂云耳。盖如认人心作道心。则即所谓杂也。是以于中庸序说。亦曰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盖必曰。二者之间。然后杂字意方分明。而今乃只曰不杂于形气之私。则设令其意。果如先生。岂不为偏持一边之归耶。窃见蔡氏之意。欲与义理之正。作为对句。而故改其语如此。然先生于此处及中庸序说。亦不作对句。每曰二者之间云云。其微意必有所在而然也。仍念先生与陈同甫书。论此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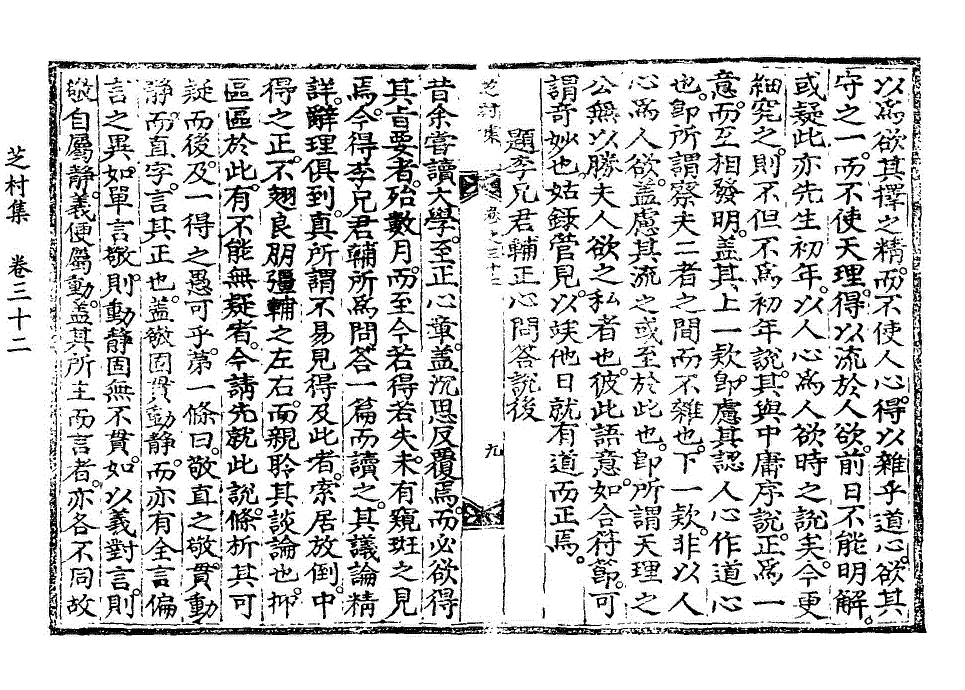 以为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前日不能明解。或疑此亦先生初年。以人心为人欲时之说矣。今更细究之。则不但不为初年说。其与中庸序说。正为一意。而互相发明。盖其上一款。即虑其认人心作道心也。即所谓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下一款。非以人心为人欲。盖虑其流之或至于此也。即所谓天理之公无以胜夫人欲之私者也。彼此语意。如合符节。可谓奇妙也。姑录管见。以俟他日就有道而正焉。
以为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前日不能明解。或疑此亦先生初年。以人心为人欲时之说矣。今更细究之。则不但不为初年说。其与中庸序说。正为一意。而互相发明。盖其上一款。即虑其认人心作道心也。即所谓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下一款。非以人心为人欲。盖虑其流之或至于此也。即所谓天理之公无以胜夫人欲之私者也。彼此语意。如合符节。可谓奇妙也。姑录管见。以俟他日就有道而正焉。题李兄君辅正心问答说后
昔余尝读大学。至正心章。盖沉思反覆焉。而必欲得其旨要者。殆数月。而至今若得若失。未有窥斑之见焉。今得李兄君辅所为问答一篇而读之。其议论精详。辞理俱到。真所谓不易见得及此者。索居放倒。中得之正。不翅良朋彊辅之左右。而亲聆其谈论也。抑区区于此。有不能无疑者。今请先就此说。条析其可疑而后。及一得之愚可乎。第一条曰。敬直之敬。贯动静。而直字。言其正也。盖敬固贯动静。而亦有全言偏言之异。如单言敬。则动静固无不贯。如以义对言。则敬自属静。义便属动。盖其所主而言者。亦各不同故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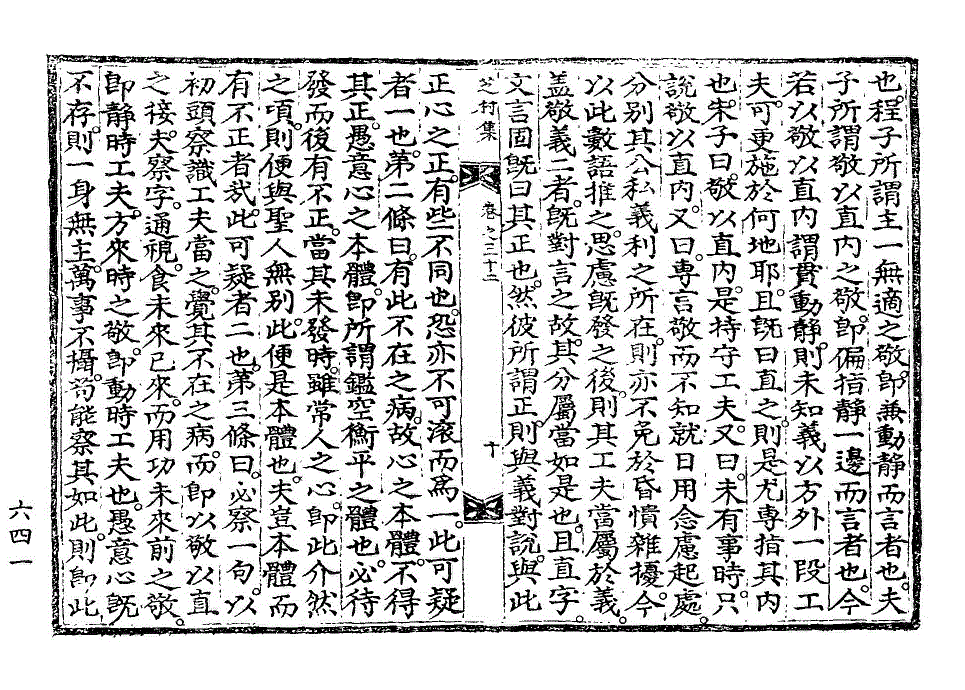 也。程子所谓主一无适之敬。即兼动静而言者也。夫子所谓敬以直内之敬。即偏指静一边而言者也。今若以敬以直内谓贯动静。则未知义以方外一段工夫。可更施于何地耶。且既曰直之。则是尤专指其内也。朱子曰。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又曰。未有事时。只说敬以直内。又曰。专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则亦不免于昏愦杂扰。今以此数语推之。思虑既发之后。则其工夫当属于义。盖敬义二者。既对言之故。其分属当如是也。且直字。文言固既曰其正也。然彼所谓正。则与义对说。与此正心之正。有些不同也。恐亦不可滚而为一。此可疑者一也。第二条曰。有此不在之病。故心之本体。不得其正。愚意心之本体。即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也。必待发而后有不正。当其未发时。虽常人之心。即此介然之顷。则便与圣人无别。此便是本体也。夫岂本体而有不正者哉。此可疑者二也。第三条曰。必察一句。以初头察识工夫当之。觉其不在之病。而即以敬以直之接。夫察字。通视。食未来已来。而用功未来前之敬。即静时工夫。方来时之敬。即动时工夫也。愚意心既不存。则一身无主。万事不摄。苟能察其如此。则即此
也。程子所谓主一无适之敬。即兼动静而言者也。夫子所谓敬以直内之敬。即偏指静一边而言者也。今若以敬以直内谓贯动静。则未知义以方外一段工夫。可更施于何地耶。且既曰直之。则是尤专指其内也。朱子曰。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又曰。未有事时。只说敬以直内。又曰。专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则亦不免于昏愦杂扰。今以此数语推之。思虑既发之后。则其工夫当属于义。盖敬义二者。既对言之故。其分属当如是也。且直字。文言固既曰其正也。然彼所谓正。则与义对说。与此正心之正。有些不同也。恐亦不可滚而为一。此可疑者一也。第二条曰。有此不在之病。故心之本体。不得其正。愚意心之本体。即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也。必待发而后有不正。当其未发时。虽常人之心。即此介然之顷。则便与圣人无别。此便是本体也。夫岂本体而有不正者哉。此可疑者二也。第三条曰。必察一句。以初头察识工夫当之。觉其不在之病。而即以敬以直之接。夫察字。通视。食未来已来。而用功未来前之敬。即静时工夫。方来时之敬。即动时工夫也。愚意心既不存。则一身无主。万事不摄。苟能察其如此。则即此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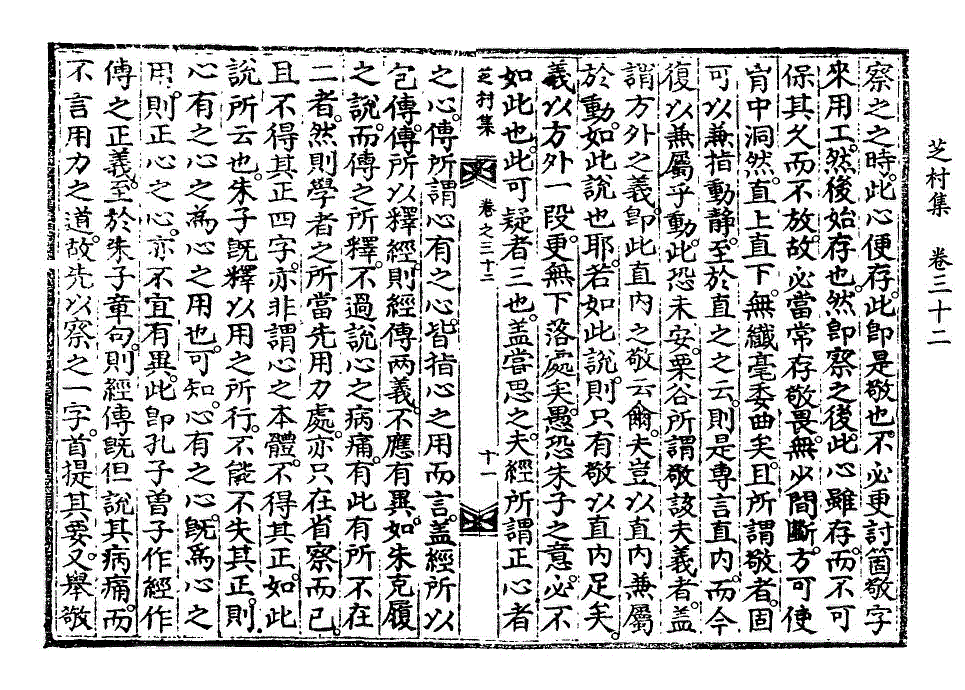 察之之时。此心便存。此即是敬也。不必更讨个敬字来用工。然后始存也。然即察之后。此心虽存。而不可保其久而不放。故必当常存敬畏。无少间断。方可使胸中洞然。直上直下。无纤毫委曲矣。且所谓敬者。固可以兼指动静。至于直之之云。则是专言直内。而今复以兼属乎动。此恐未安。栗谷所谓敬该夫义者。盖谓方外之义。即此直内之敬云尔。夫岂以直内兼属于动。如此说也耶。若如此说。则只有敬以直内足矣。义以方外一段。更无下落处矣。愚恐朱子之意。必不如此也。此可疑者三也。盖尝思之。夫经所谓正心者之心。传所谓心有之心。皆指心之用而言。盖经所以包传。传所以释经。则经传两义。不应有异。如朱克履之说。而传之所释。不过说心之病痛。有此有所不在二者。然则学者之所当先用力处。亦只在省察而已。且不得其正四字。亦非谓心之本体。不得其正。如此说所云也。朱子既释以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则心有之心之为心之用也。可知。心有之心。既为心之用。则正心之心。亦不宜有异。此即孔子曾子作经作传之正义。至于朱子章句。则经传既但说其病痛。而不言用力之道。故先以察之一字。首提其要。又举敬
察之之时。此心便存。此即是敬也。不必更讨个敬字来用工。然后始存也。然即察之后。此心虽存。而不可保其久而不放。故必当常存敬畏。无少间断。方可使胸中洞然。直上直下。无纤毫委曲矣。且所谓敬者。固可以兼指动静。至于直之之云。则是专言直内。而今复以兼属乎动。此恐未安。栗谷所谓敬该夫义者。盖谓方外之义。即此直内之敬云尔。夫岂以直内兼属于动。如此说也耶。若如此说。则只有敬以直内足矣。义以方外一段。更无下落处矣。愚恐朱子之意。必不如此也。此可疑者三也。盖尝思之。夫经所谓正心者之心。传所谓心有之心。皆指心之用而言。盖经所以包传。传所以释经。则经传两义。不应有异。如朱克履之说。而传之所释。不过说心之病痛。有此有所不在二者。然则学者之所当先用力处。亦只在省察而已。且不得其正四字。亦非谓心之本体。不得其正。如此说所云也。朱子既释以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则心有之心之为心之用也。可知。心有之心。既为心之用。则正心之心。亦不宜有异。此即孔子曾子作经作传之正义。至于朱子章句。则经传既但说其病痛。而不言用力之道。故先以察之一字。首提其要。又举敬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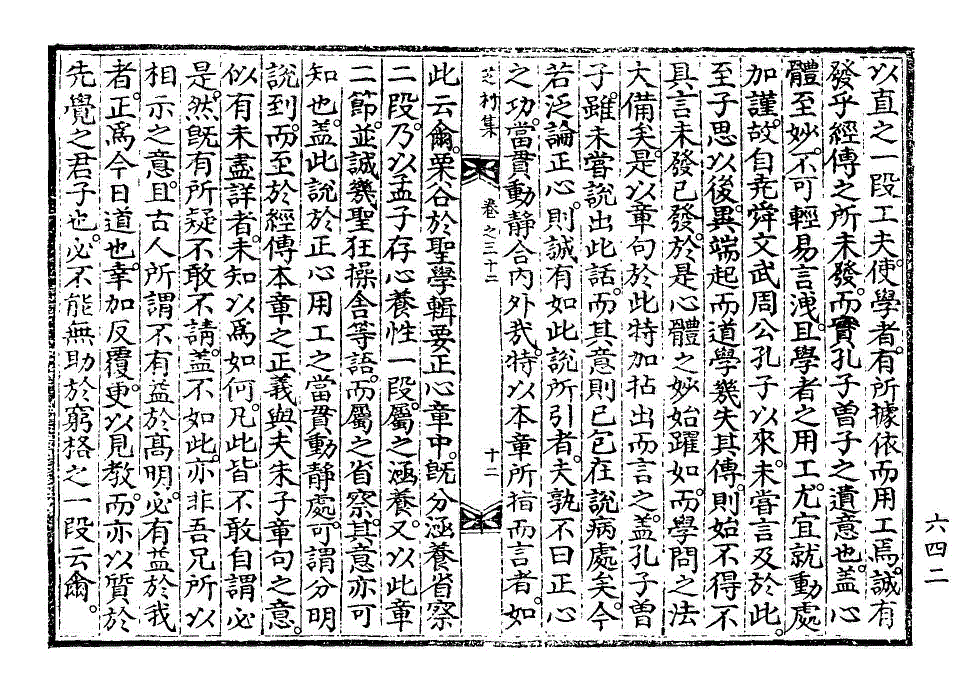 以直之一段工夫。使学者。有所据依而用工焉。诚有发乎经传之所未发。而实孔子曾子之遗意也。盖心体至妙。不可轻易言泄。且学者之用工。尤宜就动处加谨。故自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未尝言及于此。至子思以后。异端起而道学几失其传。则始不得不具言未发已发。于是心体之妙始跃如。而学问之法大备矣。是以章句于此特加拈出而言之。盖孔子曾子。虽未尝说出此话。而其意则已包在说病处矣。今若泛论正心。则诚有如此说所引者。夫孰不曰正心之功。当贯动静合内外哉。特以本章所指而言者。如此云尔。栗谷于圣学辑要正心章中。既分涵养省察二段。乃以孟子存心养性一段。属之涵养。又以此章二节。并诚几圣狂操舍等语。而属之省察。其意亦可知也。盖此说于正心用工之当贯动静处。可谓分明说到。而至于经传本章之正义与夫朱子章句之意。似有未尽详者。未知以为如何。凡此皆不敢自谓必是。然既有所疑不敢不请。盖不如此。亦非吾兄所以相示之意。且古人所谓不有益于高明。必有益于我者。正为今日道也。幸加反覆。更以见教。而亦以质于先觉之君子也。必不能无助于穷格之一段云尔。
以直之一段工夫。使学者。有所据依而用工焉。诚有发乎经传之所未发。而实孔子曾子之遗意也。盖心体至妙。不可轻易言泄。且学者之用工。尤宜就动处加谨。故自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未尝言及于此。至子思以后。异端起而道学几失其传。则始不得不具言未发已发。于是心体之妙始跃如。而学问之法大备矣。是以章句于此特加拈出而言之。盖孔子曾子。虽未尝说出此话。而其意则已包在说病处矣。今若泛论正心。则诚有如此说所引者。夫孰不曰正心之功。当贯动静合内外哉。特以本章所指而言者。如此云尔。栗谷于圣学辑要正心章中。既分涵养省察二段。乃以孟子存心养性一段。属之涵养。又以此章二节。并诚几圣狂操舍等语。而属之省察。其意亦可知也。盖此说于正心用工之当贯动静处。可谓分明说到。而至于经传本章之正义与夫朱子章句之意。似有未尽详者。未知以为如何。凡此皆不敢自谓必是。然既有所疑不敢不请。盖不如此。亦非吾兄所以相示之意。且古人所谓不有益于高明。必有益于我者。正为今日道也。幸加反覆。更以见教。而亦以质于先觉之君子也。必不能无助于穷格之一段云尔。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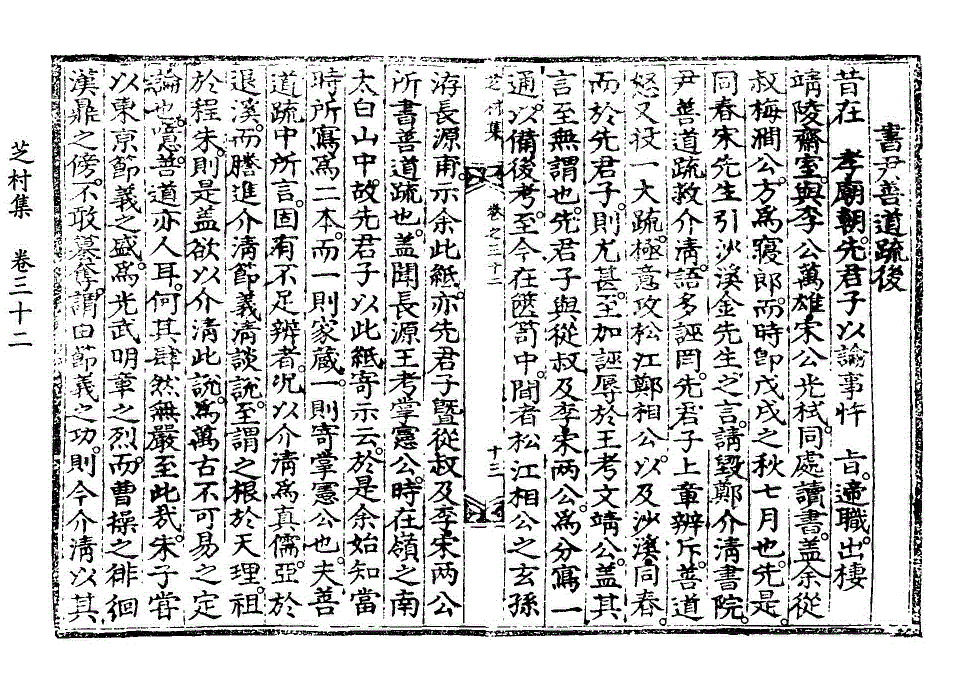 书尹善道疏后
书尹善道疏后昔在 孝庙朝。先君子以论事忤 旨。遆职。出栖 靖陵斋室。与李公万雄,宋公光栻。同处读书。盖余从叔梅涧公。方为寝郎。而时即戊戌之秋七月也。先是。同春宋先生引沙溪金先生之言。请毁郑介清书院。尹善道疏救介清。语多诬罔。先君子上章辨斥。善道怒又投一大疏。极意攻松江郑相公。以及沙溪,同春。而于先君子。则尤甚。至加诬辱于王考文靖公。盖其言至无谓也。先君子与从叔及李,宋两公。为分写一通。以备后考。至今在箧笥中。间者松江相公之玄孙荐长源甫。示余此纸。亦先君子暨从叔及李,宋两公所书善道疏也。盖闻长源王考掌宪公。时在岭之南太白山中。故先君子以此纸寄示云。于是余始知当时所写为二本。而一则家藏。一则寄掌宪公也。夫善道疏中所言。固有不足辨者。况以介清为真儒。亚于退溪。而誊进介清节义清谈说。至谓之根于天理。祖于程朱。则是盖欲以介清此说。为万古不可易之定论也。噫。善道亦人耳。何其肆然无严至此哉。朱子尝以东京节义之盛。为光武明章之烈。而曹操之徘徊汉鼎之傍。不敢篡夺。谓由节义之功。则今介清以其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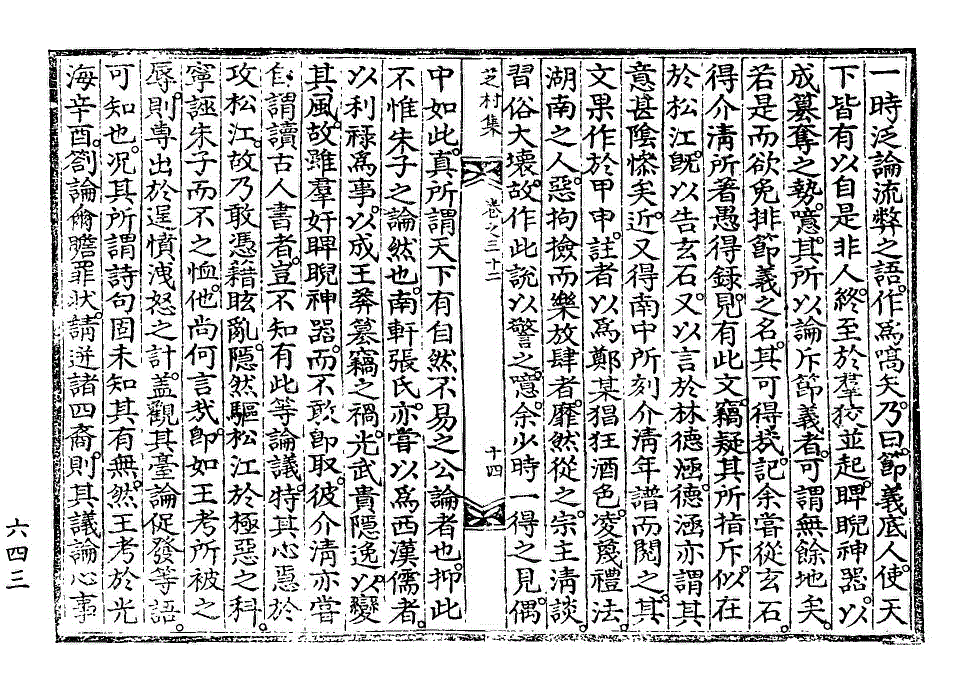 一时泛论流弊之语。作为嗃矢。乃曰。节义底人。使天下皆有以自是非人。终至于群狡并起。睥睨神器。以成篡夺之势。噫。其所以论斥节义者。可谓无馀地矣。若是而欲免排节义之名。其可得哉。记余尝从玄石。得介清所著愚得录。见有此文。窃疑其所指斥。似在于松江。既以告玄石。又以言于林德涵。德涵亦谓其意甚阴惨矣。近又得南中所刻介清年谱而阅之。其文果作于甲申。注者以为郑某猖狂酒色。凌蔑礼法。湖南之人。恶拘检而乐放肆者。靡然从之。宗主清谈。习俗大坏。故作此说以警之。噫。余少时一得之见。偶中如此。真所谓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论者也。抑此不惟朱子之论然也。南轩张氏。亦尝以为西汉儒者。以利禄为事。以成王莽篡窃之祸。光武贵隐逸。以变其风。故虽群奸睥睨神器。而不敢即取。彼介清亦尝自谓读古人书者。岂不知有此等论议。特其心急于攻松江。故乃敢凭藉眩乱。隐然驱松江于极恶之科。宁诬朱子而不之恤。他尚何言哉。即如王考所被之辱。则专出于逞愤泄怒之计。盖观其台论促发等语。可知也。况其所谓诗句固未知其有无。然王考于光海辛酉。劄论尔瞻罪状。请迸诸四裔。则其议论心事
一时泛论流弊之语。作为嗃矢。乃曰。节义底人。使天下皆有以自是非人。终至于群狡并起。睥睨神器。以成篡夺之势。噫。其所以论斥节义者。可谓无馀地矣。若是而欲免排节义之名。其可得哉。记余尝从玄石。得介清所著愚得录。见有此文。窃疑其所指斥。似在于松江。既以告玄石。又以言于林德涵。德涵亦谓其意甚阴惨矣。近又得南中所刻介清年谱而阅之。其文果作于甲申。注者以为郑某猖狂酒色。凌蔑礼法。湖南之人。恶拘检而乐放肆者。靡然从之。宗主清谈。习俗大坏。故作此说以警之。噫。余少时一得之见。偶中如此。真所谓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论者也。抑此不惟朱子之论然也。南轩张氏。亦尝以为西汉儒者。以利禄为事。以成王莽篡窃之祸。光武贵隐逸。以变其风。故虽群奸睥睨神器。而不敢即取。彼介清亦尝自谓读古人书者。岂不知有此等论议。特其心急于攻松江。故乃敢凭藉眩乱。隐然驱松江于极恶之科。宁诬朱子而不之恤。他尚何言哉。即如王考所被之辱。则专出于逞愤泄怒之计。盖观其台论促发等语。可知也。况其所谓诗句固未知其有无。然王考于光海辛酉。劄论尔瞻罪状。请迸诸四裔。则其议论心事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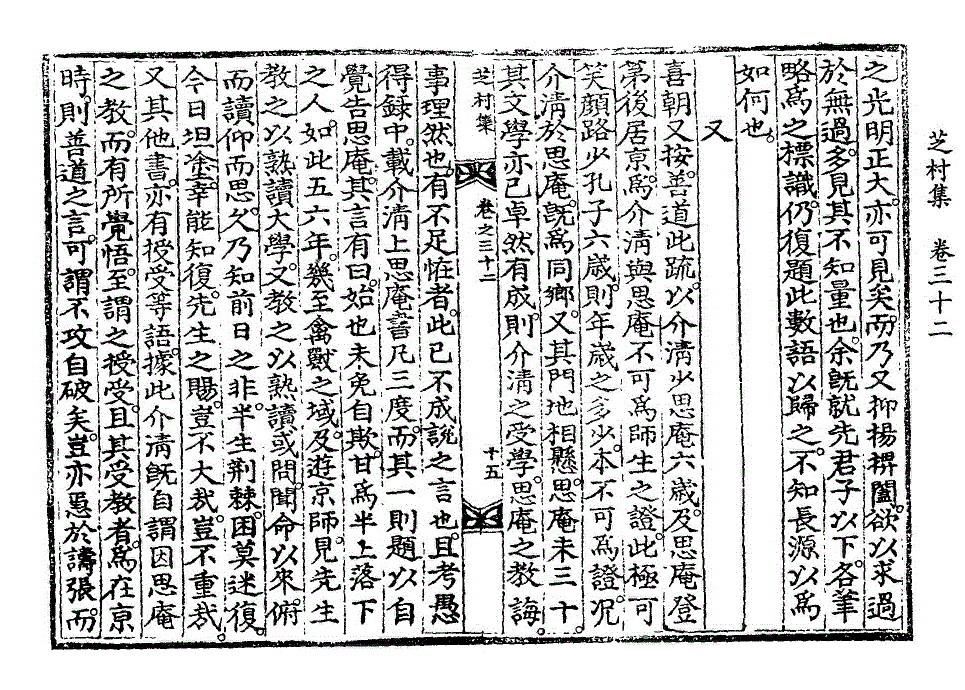 之光明正大。亦可见矣。而乃又抑扬捭阖。欲以求过于无过。多见其不知量也。余既就先君子以下。各笔略为之标识。仍复题此数语以归之。不知长源以为如何也。
之光明正大。亦可见矣。而乃又抑扬捭阖。欲以求过于无过。多见其不知量也。余既就先君子以下。各笔略为之标识。仍复题此数语以归之。不知长源以为如何也。书尹善道疏后
喜朝又按。善道此疏。以介清少思庵六岁。及思庵登第后居京。为介清与思庵不可为师生之證。此极可笑颜路少孔子六岁。则年岁之多少。本不可为證。况介清于思庵。既为同乡。又其门地相悬。思庵未三十。其文学亦已卓然有成。则介清之受学。思庵之教诲。事理然也。有不足怪者。此已不成说之言也。且考愚得录中。载介清上思庵书凡三度。而其一则题以自觉告思庵。其言有曰。始也未免自欺。甘为半上落下之人。如此五六年。几至禽兽之域。及游京师。见先生教之以熟读大学。又教之以熟读或问。闻命以来。俯而读仰而思。久乃知前日之非。半生荆棘。困莫迷复。今日坦涂。幸能知复。先生之赐。岂不大哉。岂不重哉。又其他书。亦有授受等语。据此介清既自谓因思庵之教。而有所觉悟。至谓之授受。且其受教者。为在京时。则善道之言。可谓不攻自破矣。岂亦急于诪张。而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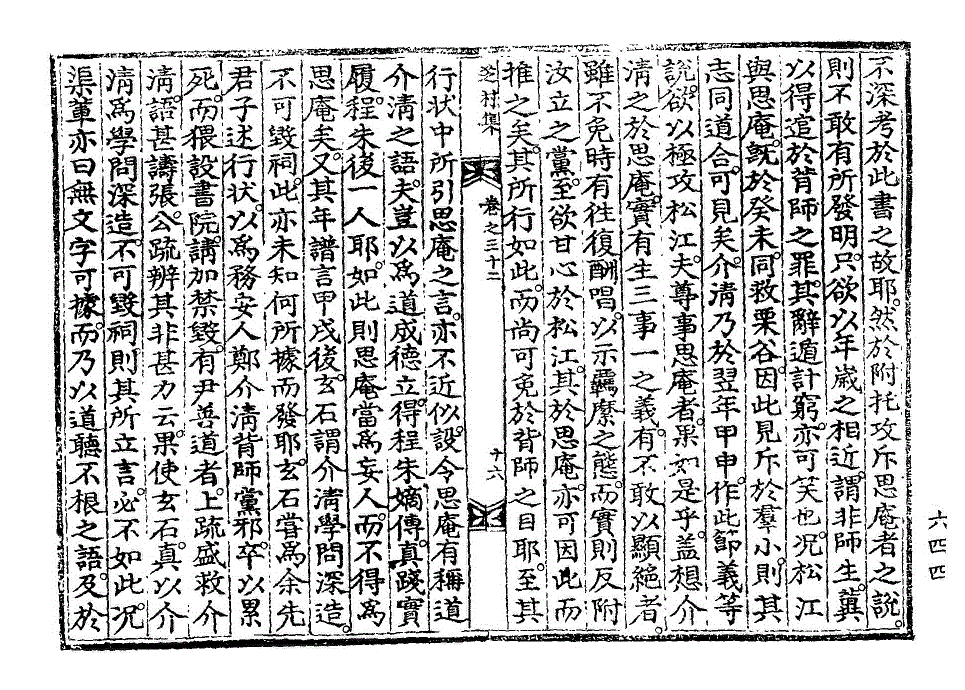 不深考于此书之故耶。然于附托攻斥思庵者之说。则不敢有所发明。只欲以年岁之相近。谓非师生。冀以得逭于背师之罪。其辞遁计穷。亦可笑也。况松江与思庵。既于癸未。同救栗谷。因此见斥于群小。则其志同道合。可见矣。介清乃于翌年甲申。作此节义等说。欲以极攻松江。夫尊事思庵者。果如是乎。盖想介清之于思庵。实有生三事一之义。有不敢以显绝者。虽不免时有往复酬唱。以示羁縻之态。而实则反附汝立之党。至欲甘心于松江。其于思庵。亦可因此而推之矣。其所行如此。而尚可免于背师之目耶。至其行状中所引思庵之言。亦不近似。设令思庵有称道介清之语。夫岂以为道成德立。得程朱嫡传。真践实履。程朱后一人耶。如此则思庵当为妄人。而不得为思庵矣。又其年谱言甲戌后。玄石谓介清学问深造。不可毁祠。此亦未知何所据而发耶。玄石尝为余先君子述行状。以为务安人郑介清背师党邪。卒以累死。而猥设书院。请加禁毁。有尹善道者。上疏盛救介清。语甚诪张。公疏辨其非甚力云。果使玄石。真以介清为学问深造。不可毁祠。则其所立言。必不如此。况渠辈亦曰无文字可据。而乃以道听不根之语。及于
不深考于此书之故耶。然于附托攻斥思庵者之说。则不敢有所发明。只欲以年岁之相近。谓非师生。冀以得逭于背师之罪。其辞遁计穷。亦可笑也。况松江与思庵。既于癸未。同救栗谷。因此见斥于群小。则其志同道合。可见矣。介清乃于翌年甲申。作此节义等说。欲以极攻松江。夫尊事思庵者。果如是乎。盖想介清之于思庵。实有生三事一之义。有不敢以显绝者。虽不免时有往复酬唱。以示羁縻之态。而实则反附汝立之党。至欲甘心于松江。其于思庵。亦可因此而推之矣。其所行如此。而尚可免于背师之目耶。至其行状中所引思庵之言。亦不近似。设令思庵有称道介清之语。夫岂以为道成德立。得程朱嫡传。真践实履。程朱后一人耶。如此则思庵当为妄人。而不得为思庵矣。又其年谱言甲戌后。玄石谓介清学问深造。不可毁祠。此亦未知何所据而发耶。玄石尝为余先君子述行状。以为务安人郑介清背师党邪。卒以累死。而猥设书院。请加禁毁。有尹善道者。上疏盛救介清。语甚诪张。公疏辨其非甚力云。果使玄石。真以介清为学问深造。不可毁祠。则其所立言。必不如此。况渠辈亦曰无文字可据。而乃以道听不根之语。及于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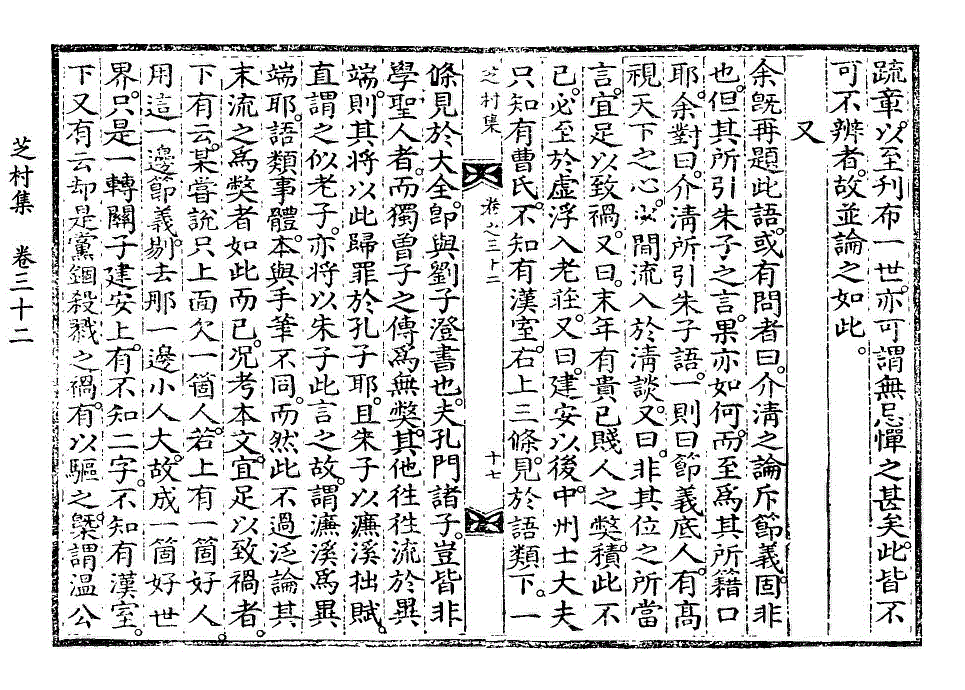 疏章。以至刊布一世。亦可谓无忌惮之甚矣。此皆不可不辨者。故并论之如此。
疏章。以至刊布一世。亦可谓无忌惮之甚矣。此皆不可不辨者。故并论之如此。书尹善道疏后
余既再题此语。或有问者曰。介清之论斥节义。固非也。但其所引朱子之言。果亦如何。而至为其所籍口耶。余对曰。介清所引朱子语。一则曰节义底人。有高视天下之心。少间流入于清谈。又曰。非其位之所当言。宜足以致祸。又曰。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积此不已。必至于虚浮入老庄。又曰。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右上三条。见于语类下。一条见于大全。即与刘子澄书也。夫孔门诸子。岂皆非学圣人者。而独曾子之传为无弊。其他往往流于异端。则其将以此归罪于孔子耶。且朱子以濂溪拙赋。直谓之似老子。亦将以朱子此言之故。谓濂溪为异端耶。语类事体。本与手笔不同。而然此不过泛论其末流之为弊者如此而已。况考本文。宜足以致祸者。下有云。某尝说只上面欠一个人。若上有一个好人。用这一边节义。剔去那一边小人大。故成一个好世界。只是一转关子建安上。有不知二字。不知有汉室。下又有云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槩谓温公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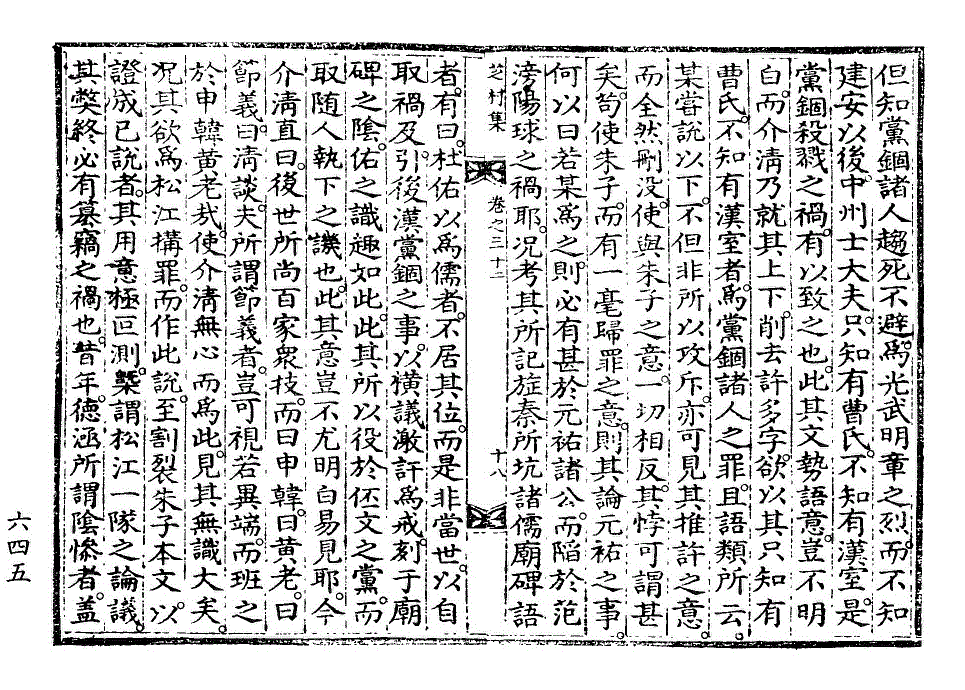 但知党锢诸人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致之也。此其文势语意。岂不明白。而介清乃就其上下。削去许多字。欲以其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者。为党锢诸人之罪。且语类所云。某尝说以下。不但非所以攻斥。亦可见其推许之意。而全然删没。使与朱子之意。一切相反。其悖可谓甚矣。苟使朱子。而有一毫归罪之意。则其论元祐之事。何以曰若某为之。则必有甚于元祐诸公。而陷于范滂,阳球之祸耶。况考其所记旌秦所坑诸儒庙碑语者。有曰。杜佑以为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当世。以自取祸及。引后汉党锢之事。以横议激讦为戒。刻于庙碑之阴。佑之识趣如此。此其所以役于伾文之党。而取随人执下之讥也。此其意岂不尤明白易见耶。今介清直曰。后世所尚百家众技。而曰申韩。曰黄老。曰节义。曰清谈。夫所谓节义者。岂可视若异端。而班之于申韩黄老哉。使介清无心而为此。见其无识大矣。况其欲为松江搆罪。而作此说。至割裂朱子本文。以證成己说者。其用意极叵测。槩谓松江一队之论议。其弊终必有篡窃之祸也。昔年。德涵所谓阴惨者。盖
但知党锢诸人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致之也。此其文势语意。岂不明白。而介清乃就其上下。削去许多字。欲以其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者。为党锢诸人之罪。且语类所云。某尝说以下。不但非所以攻斥。亦可见其推许之意。而全然删没。使与朱子之意。一切相反。其悖可谓甚矣。苟使朱子。而有一毫归罪之意。则其论元祐之事。何以曰若某为之。则必有甚于元祐诸公。而陷于范滂,阳球之祸耶。况考其所记旌秦所坑诸儒庙碑语者。有曰。杜佑以为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当世。以自取祸及。引后汉党锢之事。以横议激讦为戒。刻于庙碑之阴。佑之识趣如此。此其所以役于伾文之党。而取随人执下之讥也。此其意岂不尤明白易见耶。今介清直曰。后世所尚百家众技。而曰申韩。曰黄老。曰节义。曰清谈。夫所谓节义者。岂可视若异端。而班之于申韩黄老哉。使介清无心而为此。见其无识大矣。况其欲为松江搆罪。而作此说。至割裂朱子本文。以證成己说者。其用意极叵测。槩谓松江一队之论议。其弊终必有篡窃之祸也。昔年。德涵所谓阴惨者。盖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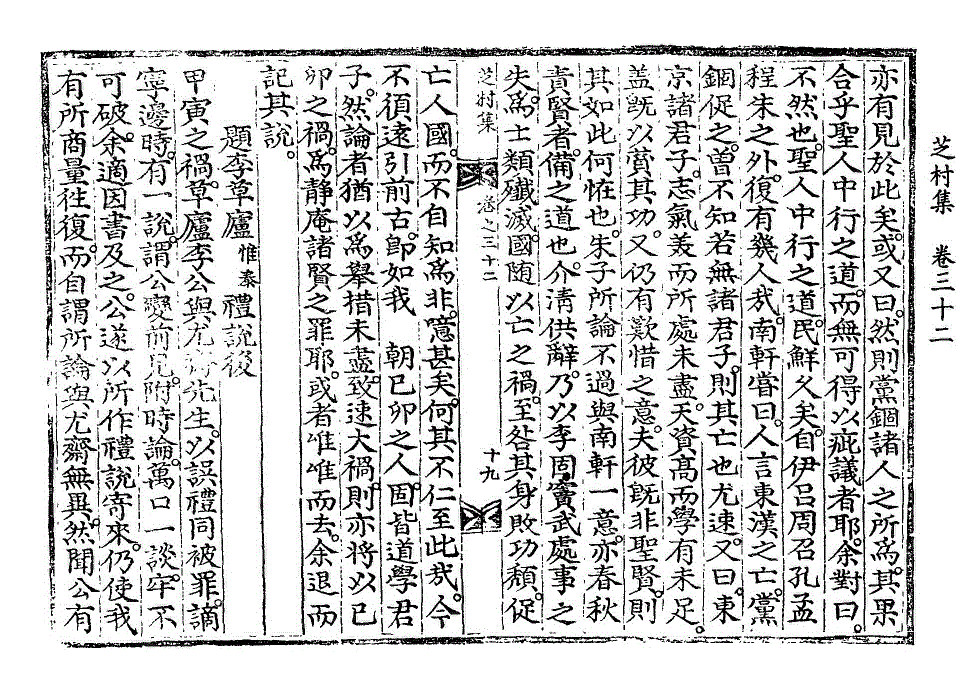 亦有见于此矣。或又曰。然则党锢诸人之所为。其果合乎圣人中行之道。而无可得以疵议者耶。余对曰。不然也。圣人中行之道。民鲜久矣。自伊吕周召孔孟程朱之外。复有几人哉。南轩尝曰。人言东汉之亡。党锢促之。曾不知若无诸君子。则其亡也尤速。又曰。东京诸君子。志气美而所处未尽。天资高而学有未足。盖既以赞其功。又仍有叹惜之意。夫彼既非圣贤。则其如此何怪也。朱子所论不过与南轩一意。亦春秋责贤者。备之道也。介清供辞。乃以李固,窦武处事之失。为士类歼灭。国随以亡之祸。至咎其身败功颓。促亡人国。而不自知为非。噫甚矣。何其不仁至此哉。今不须远引前古。即如我 朝己卯之人。固皆道学君子。然论者犹以为举措未尽。致速大祸。则亦将以己卯之祸。为静庵诸贤之罪耶。或者唯唯而去。余退而记其说。
亦有见于此矣。或又曰。然则党锢诸人之所为。其果合乎圣人中行之道。而无可得以疵议者耶。余对曰。不然也。圣人中行之道。民鲜久矣。自伊吕周召孔孟程朱之外。复有几人哉。南轩尝曰。人言东汉之亡。党锢促之。曾不知若无诸君子。则其亡也尤速。又曰。东京诸君子。志气美而所处未尽。天资高而学有未足。盖既以赞其功。又仍有叹惜之意。夫彼既非圣贤。则其如此何怪也。朱子所论不过与南轩一意。亦春秋责贤者。备之道也。介清供辞。乃以李固,窦武处事之失。为士类歼灭。国随以亡之祸。至咎其身败功颓。促亡人国。而不自知为非。噫甚矣。何其不仁至此哉。今不须远引前古。即如我 朝己卯之人。固皆道学君子。然论者犹以为举措未尽。致速大祸。则亦将以己卯之祸。为静庵诸贤之罪耶。或者唯唯而去。余退而记其说。题李草庐(惟泰)礼说后
甲寅之祸。草庐李公与尤斋先生。以误礼同被罪。谪宁边时。有一说。谓公变前见。附时论。万口一谈。牢不可破。余适因书及之。公遂以所作礼说寄来。仍使我有所商量往复。而自谓所论与尤斋无异。然闻公有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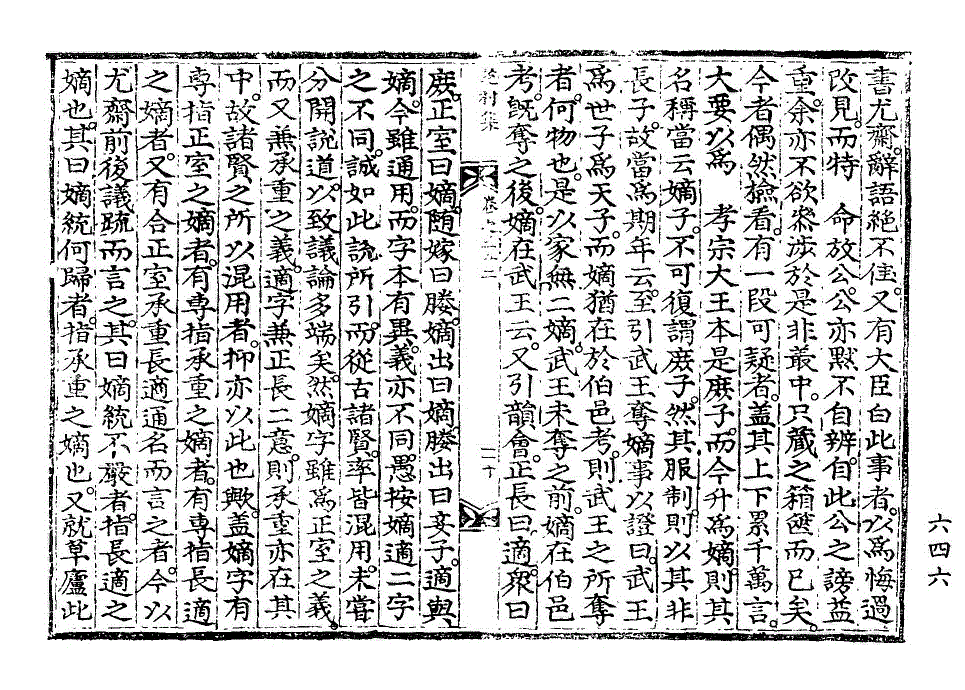 书尤斋。辞语绝不佳。又有大臣白此事者。以为悔过改见。而特 命放公。公亦默不自辨。自此公之谤益重。余亦不欲参涉于是非丛中。只藏之箱箧而已矣。今者偶然检看。有一段可疑者。盖其上下累千万言。大要以为 孝宗大王本是庶子。而今升为嫡。则其名称当云嫡子。不可复谓庶子。然其服制。则以其非长子。故当为期年云。至引武王夺嫡事以證曰。武王为世子为天子。而嫡犹在于伯邑考。则武王之所夺者。何物也。是以家无二嫡。武王未夺之前。嫡在伯邑考。既夺之后。嫡在武王云。又引韵会。正长曰。适。众曰庶。正室曰嫡。随嫁曰媵。嫡出曰嫡。媵出曰妾子。适与嫡。今虽通用。而字本有异。义亦不同。愚按嫡适二字之不同。诚如此说所引。而从古诸贤。率皆混用。未尝分开说道。以致议论多端矣。然嫡字虽为正室之义。而又兼承重之义。适字兼正长二意。则承重亦在其中。故诸贤之所以混用者。抑亦以此也欤。盖嫡字有专指正室之嫡者。有专指承重之嫡者。有专指长适之嫡者。又有合正室承重长适通名而言之者。今以尤斋前后议疏而言之。其曰嫡统不严者。指长适之嫡也。其曰嫡统何归者。指承重之嫡也。又就草庐此
书尤斋。辞语绝不佳。又有大臣白此事者。以为悔过改见。而特 命放公。公亦默不自辨。自此公之谤益重。余亦不欲参涉于是非丛中。只藏之箱箧而已矣。今者偶然检看。有一段可疑者。盖其上下累千万言。大要以为 孝宗大王本是庶子。而今升为嫡。则其名称当云嫡子。不可复谓庶子。然其服制。则以其非长子。故当为期年云。至引武王夺嫡事以證曰。武王为世子为天子。而嫡犹在于伯邑考。则武王之所夺者。何物也。是以家无二嫡。武王未夺之前。嫡在伯邑考。既夺之后。嫡在武王云。又引韵会。正长曰。适。众曰庶。正室曰嫡。随嫁曰媵。嫡出曰嫡。媵出曰妾子。适与嫡。今虽通用。而字本有异。义亦不同。愚按嫡适二字之不同。诚如此说所引。而从古诸贤。率皆混用。未尝分开说道。以致议论多端矣。然嫡字虽为正室之义。而又兼承重之义。适字兼正长二意。则承重亦在其中。故诸贤之所以混用者。抑亦以此也欤。盖嫡字有专指正室之嫡者。有专指承重之嫡者。有专指长适之嫡者。又有合正室承重长适通名而言之者。今以尤斋前后议疏而言之。其曰嫡统不严者。指长适之嫡也。其曰嫡统何归者。指承重之嫡也。又就草庐此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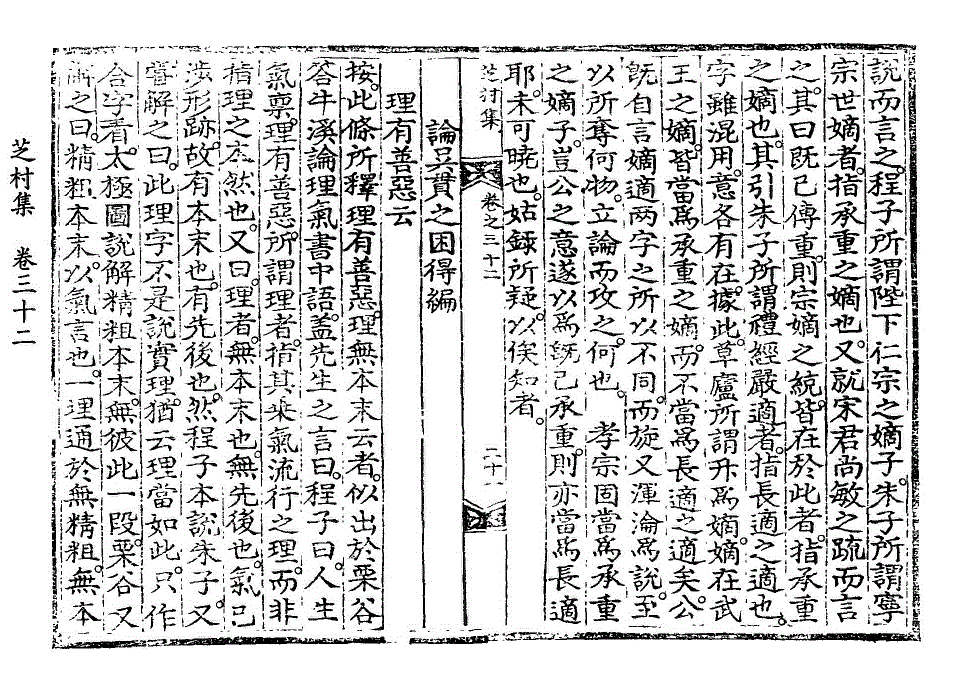 说而言之。程子所谓陛下仁宗之嫡子。朱子所谓宁宗世嫡者。指承重之嫡也。又就宋君尚敏之疏而言之。其曰既已传重。则宗嫡之统。皆在于此者。指承重之嫡也。其引朱子所谓礼经严适者。指长适之适也。字虽混用。意各有在。据此。草庐所谓升为嫡。嫡在武王之嫡。皆当为承重之嫡。而不当为长适之适矣。公既自言嫡适两字之所以不同。而旋又浑沦为说。至以所夺何物。立论而攻之。何也。 孝宗固当为承重之嫡子。岂公之意遂以为既已承重。则亦当为长适耶。未可晓也。姑录所疑。以俟知者。
说而言之。程子所谓陛下仁宗之嫡子。朱子所谓宁宗世嫡者。指承重之嫡也。又就宋君尚敏之疏而言之。其曰既已传重。则宗嫡之统。皆在于此者。指承重之嫡也。其引朱子所谓礼经严适者。指长适之适也。字虽混用。意各有在。据此。草庐所谓升为嫡。嫡在武王之嫡。皆当为承重之嫡。而不当为长适之适矣。公既自言嫡适两字之所以不同。而旋又浑沦为说。至以所夺何物。立论而攻之。何也。 孝宗固当为承重之嫡子。岂公之意遂以为既已承重。则亦当为长适耶。未可晓也。姑录所疑。以俟知者。论吴贯之困得编
理有善恶云
按。此条所释理有善恶。理无本末云者。似出于栗谷答牛溪论理气书中语。盖先生之言曰。程子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所谓理者。指其乘气流行之理。而非指理之本然也。又曰。理者。无本末也。无先后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然程子本说朱子。又尝解之曰。此理字不是说实理。犹云理当如此。只作合字看。太极图说解精粗本末。无彼此一段。栗谷又解之曰。精粗本末。以气言也。一理通于无精粗。无本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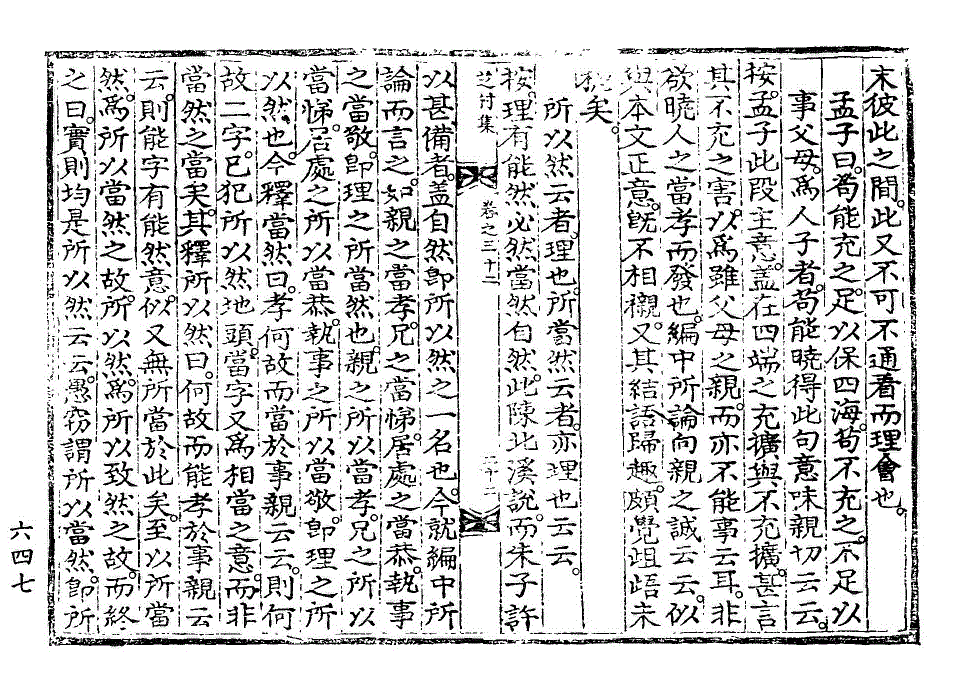 末彼此之间。此又不可不通看而理会也。
末彼此之间。此又不可不通看而理会也。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为人子者。苟能晓得此句意味亲切云云。
按。孟子此段主意。盖在四端之充扩与不充扩。甚言其不充之害。以为虽父母之亲。而亦不能事云耳。非欲晓人之当孝而发也。编中所论向亲之诚云云。似与本文正意。既不相衬。又其结语归趣。颇觉龃龉未稳矣。
所以然云者。理也。所当然云者。亦理也云云。
按。理有能然必然当然自然。此陈北溪说。而朱子许以甚备者。盖自然即所以然之一名也。今就编中所论而言之。如亲之当孝。兄之当悌。居处之当恭。执事之当敬。即理之所当然也。亲之所以当孝。兄之所以当悌。居处之所以当恭。执事之所以当敬。即理之所以然也。今释当然曰。孝何故而当于事亲云云。则何故二字。已犯所以然地头。当字又为相当之意。而非当然之当矣。其释所以然曰。何故而能孝于事亲云云。则能字有能然意。似又无所当于此矣。至以所当然。为所以当然之故。所以然。为所以致然之故。而终之曰。实则均是所以然云云。愚窃谓所以当然。即所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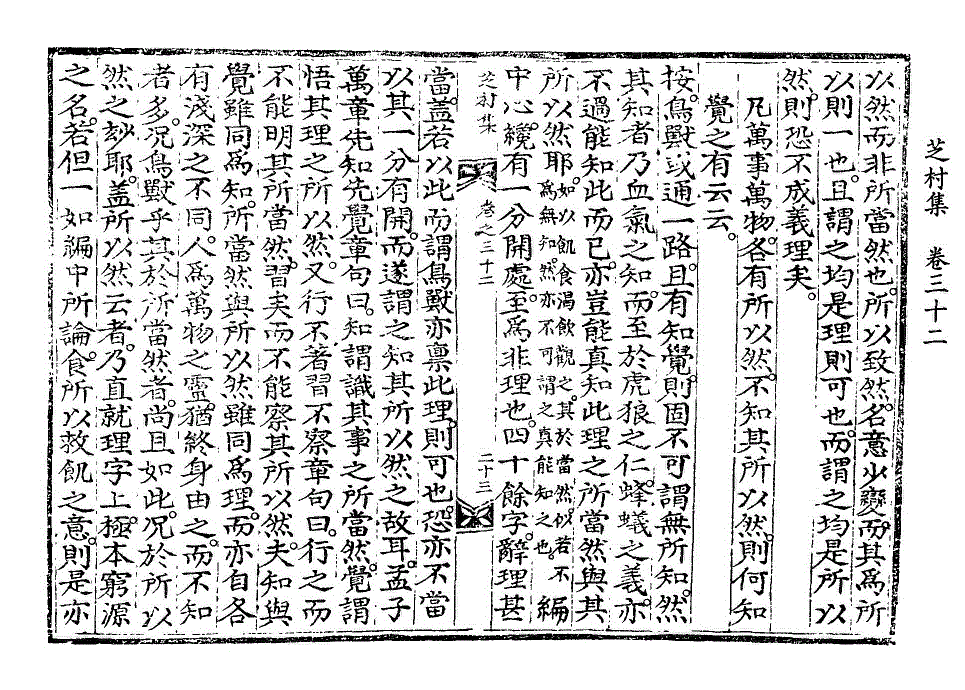 以然而非所当然也。所以致然。名意少变。而其为所以则一也。且谓之均是理则可也。而谓之均是所以然。则恐不成义理矣。
以然而非所当然也。所以致然。名意少变。而其为所以则一也。且谓之均是理则可也。而谓之均是所以然。则恐不成义理矣。凡万事万物。各有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则何知觉之有云云。
按。鸟兽或通一路。且有知觉。则固不可谓无所知。然其知者乃血气之知。而至于虎狼之仁。蜂蚁之义。亦不过能知此而已。亦岂能真知此理之所当然与其所以然耶。(如以饥食渴饮观之。其于当然。似若不为无知。然亦不可谓之真能知之也。)编中心。才有一分开处。至为非理也。四十馀字。辞理甚当。盖若以此而谓鸟兽亦禀此理。则可也。恐亦不当以其一分有开。而遂谓之知其所以然之故耳。孟子万章先知先觉章句曰。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又行不著习不察章句曰。行之而不能明其所当然。习矣而不能察其所以然。夫知与觉虽同为知。所当然与所以然虽同为理。而亦自各有浅深之不同。人为万物之灵。犹终身由之。而不知者多。况鸟兽乎其于所当然者。尚且如此。况于所以然之妙耶。盖所以然云者。乃直就理字上。极本穷源之名。若但一如编中所论。食所以救饥之意。则是亦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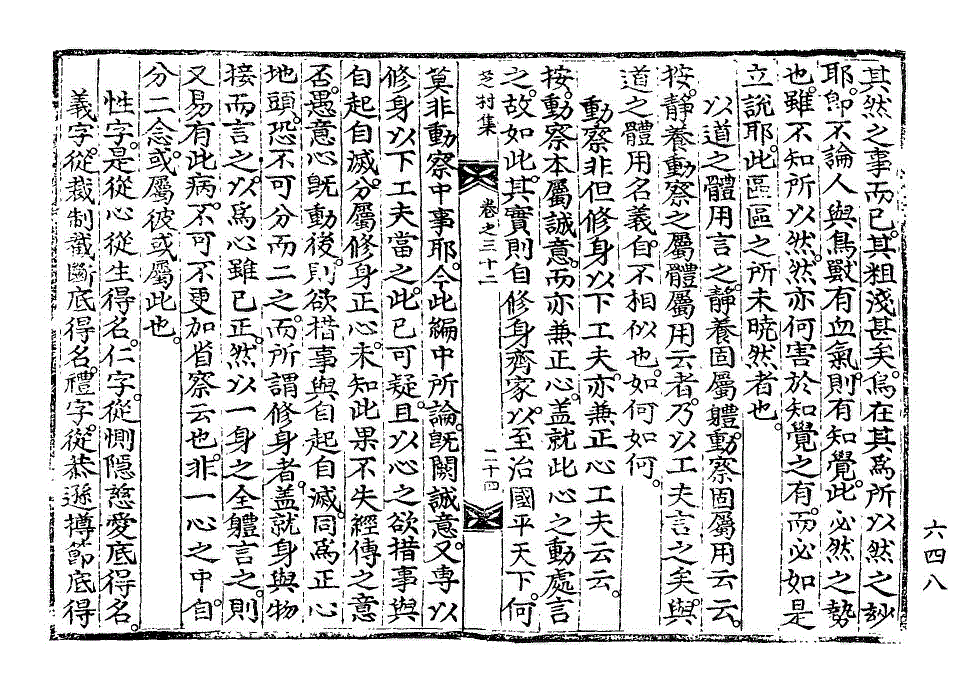 其然之事而已。其粗浅甚矣。乌在其为所以然之妙耶。即不论人与鸟兽有血气。则有知觉。此必然之势也。虽不知所以然。然亦何害于知觉之有。而必如是立说耶。此区区之所未晓然者也。
其然之事而已。其粗浅甚矣。乌在其为所以然之妙耶。即不论人与鸟兽有血气。则有知觉。此必然之势也。虽不知所以然。然亦何害于知觉之有。而必如是立说耶。此区区之所未晓然者也。以道之体用言之。静养固属体。动察固属用云云。
按。静养动察之属体属用云者。乃以工夫言之矣。与道之体用名义。自不相似也。如何如何。
动察非但修身以下工夫。亦兼正心工夫云云。
按。动察本属诚意。而亦兼正心。盖就此心之动处言之。故如此。其实则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何莫非动察中事耶。今此编中所论。既阙诚意。又专以修身以下工夫当之。此已可疑。且以心之欲措事与自起自灭。分属修身正心。未知此果不失经传之意否。愚意心既动后。则欲措事与自起自灭。同为正心地头。恐不可分而二之。而所谓修身者。盖就身与物接而言之。以为心虽已正。然以一身之全体言之。则又易有此病。不可不更加省察云也。非一心之中。自分二念。或属彼或属此也。
性字。是从心从生得名。仁字。从恻隐慈爱底得名。义字。从裁制截断底得名。礼字。从恭逊撙节底得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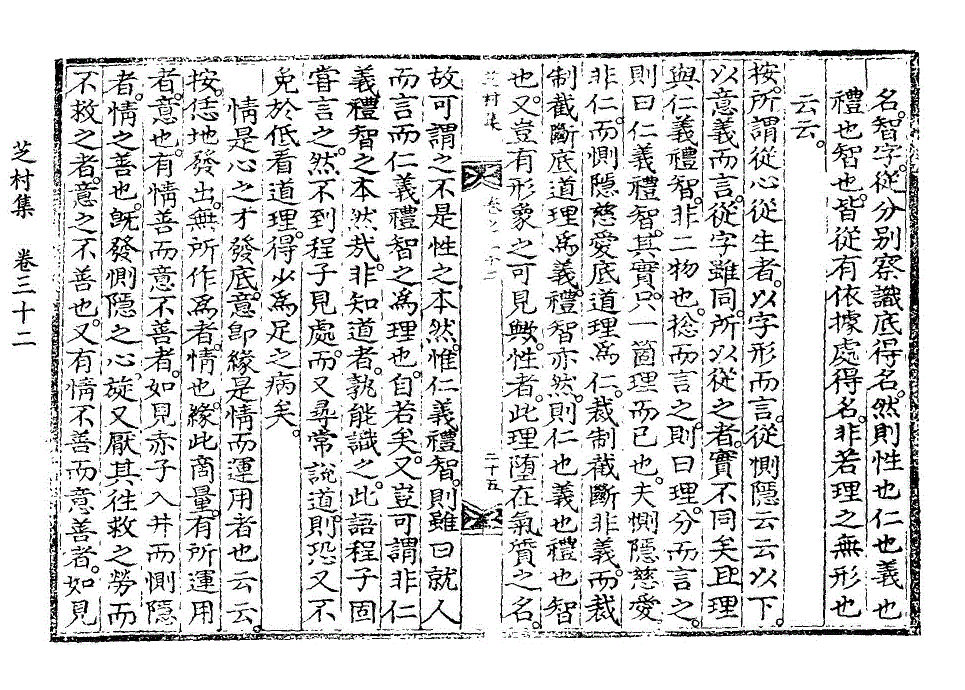 名。智字。从分别察识底得名。然则性也仁也义也礼也智也。皆从有依据处得名。非若理之无形也云云。
名。智字。从分别察识底得名。然则性也仁也义也礼也智也。皆从有依据处得名。非若理之无形也云云。按。所谓从心从生者。以字形而言。从恻隐云云以下。以意义而言。从字虽同。所以从之者。实不同矣。且理与仁义礼智。非二物也。总而言之。则曰理。分而言之。则曰仁义礼智。其实。只一个理而已也。夫恻隐慈爱非仁。而恻隐慈爱底道理为仁。裁制截断非义。而裁制截断底道理为义。礼智亦然。则仁也义也礼也智也。又岂有形象之可见欤。性者。此理堕在气质之名。故可谓之不是性之本然。惟仁义礼智。则虽曰就人而言而仁义礼智之为理也。自若矣。又岂可谓非仁义礼智之本然哉。非知道者。孰能识之。此语程子固尝言之。然不到程子见处。而又寻常说道。则恐又不免于低看道理。得少为足之病矣。
情是心之才发底。意即缘是情而运用者也云云。
按。恁地发出。无所作为者。情也。缘此商量。有所运用者。意也。有情善而意不善者。如见赤子入井而恻隐者。情之善也。既发恻隐之心。旋又厌其往救之劳而不救之者。意之不善也。又有情不善而意善者。如见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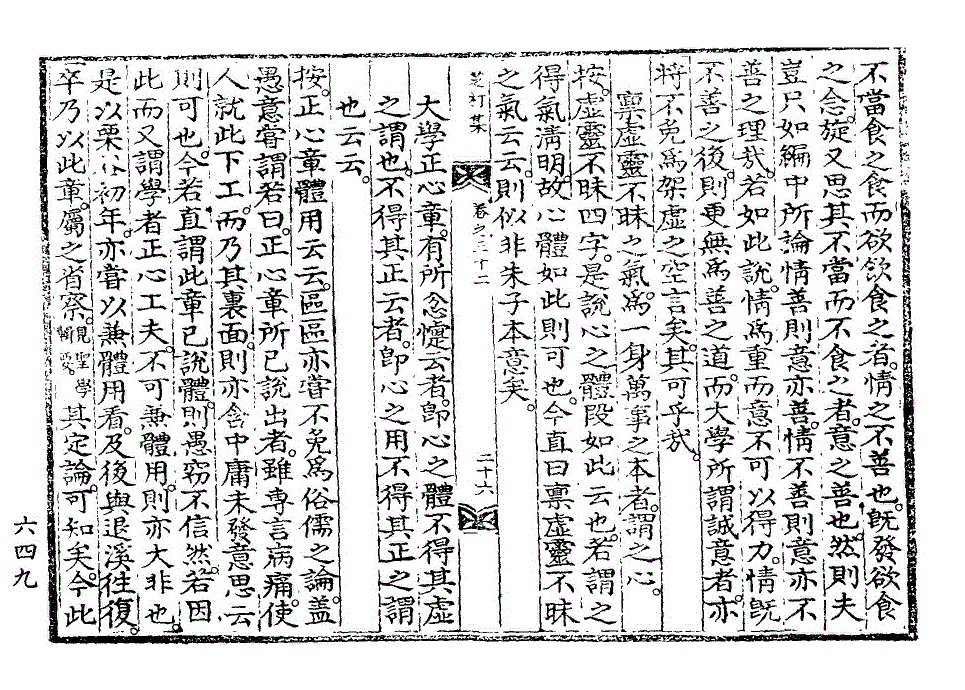 不当食之食而欲饮食之者。情之不善也。既发欲食之念。旋又思其不当而不食之者。意之善也。然则夫岂只如编中所论情善则意亦善。情不善则意亦不善之理哉。若如此说。情为重而意不可以得力。情既不善之后。则更无为善之道。而大学所谓诚意者。亦将不免为架虚之空言矣。其可乎哉。
不当食之食而欲饮食之者。情之不善也。既发欲食之念。旋又思其不当而不食之者。意之善也。然则夫岂只如编中所论情善则意亦善。情不善则意亦不善之理哉。若如此说。情为重而意不可以得力。情既不善之后。则更无为善之道。而大学所谓诚意者。亦将不免为架虚之空言矣。其可乎哉。禀虚灵不昧之气。为一身万事之本者。谓之心。
按。虚灵不昧四字。是说心之体段如此云也。若谓之得气清明。故心体如此则可也。今直曰禀虚灵不昧之气云云。则似非朱子本意矣。
大学正心章。有所忿懥云者。即心之体不得其虚之谓也。不得其正云者。即心之用不得其正之谓也云云。
按。正心章体用云云。区区亦尝不免为俗儒之论。盖愚意尝谓若曰。正心章所已说出者。虽专言病痛。使人就此下工。而乃其里面。则亦含中庸未发意思云则可也。今若直谓此章已说体。则愚窃不信然。若因此而又谓学者正心工夫。不可兼体用。则亦大非也。是以栗谷初年。亦尝以兼体用看。及后与退溪往复。卒乃以此章。属之省察。(见圣学辑要。)其定论。可知矣。今此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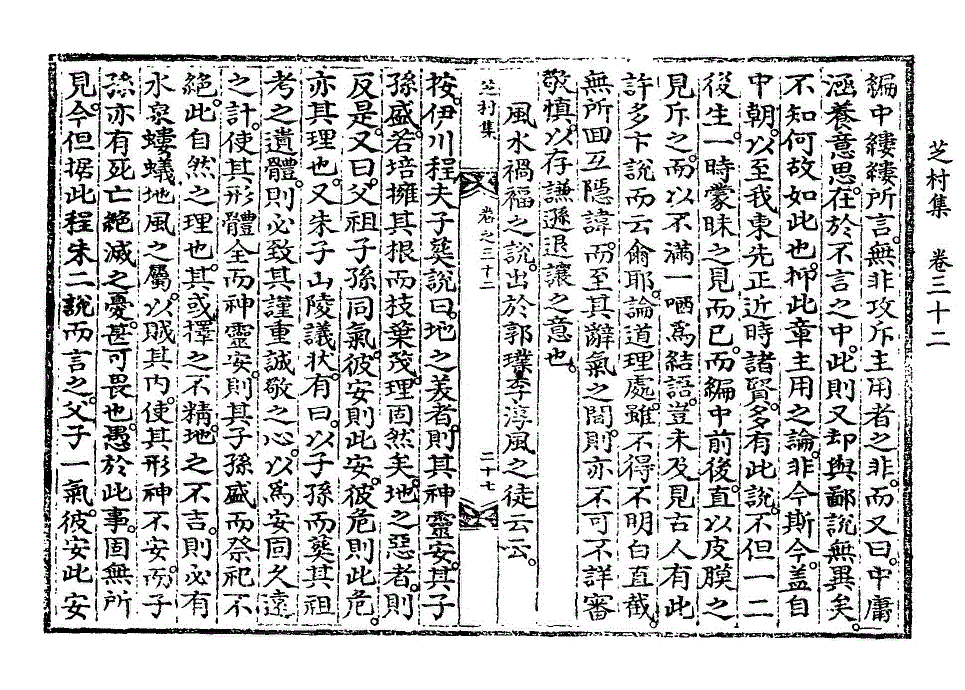 编中缕缕所言。无非攻斥主用者之非。而又曰。中庸涵养意思。在于不言之中。此则又却与鄙说无异矣。不知何故如此也。抑此章主用之论。非今斯今。盖自中朝。以至我东先正近时诸贤。多有此说。不但一二后生。一时蒙昧之见而已。而编中前后。直以皮膜之见斥之。而以不满一哂为结语。岂未及见古人有此许多卞说而云尔耶。论道理处。虽不得不明白直截。无所回互隐讳。而至其辞气之间。则亦不可不详审敬慎。以存谦逊退让之意也。
编中缕缕所言。无非攻斥主用者之非。而又曰。中庸涵养意思。在于不言之中。此则又却与鄙说无异矣。不知何故如此也。抑此章主用之论。非今斯今。盖自中朝。以至我东先正近时诸贤。多有此说。不但一二后生。一时蒙昧之见而已。而编中前后。直以皮膜之见斥之。而以不满一哂为结语。岂未及见古人有此许多卞说而云尔耶。论道理处。虽不得不明白直截。无所回互隐讳。而至其辞气之间。则亦不可不详审敬慎。以存谦逊退让之意也。风水祸福之说。出于郭璞,李淳风之徒云云。
按。伊川程夫子葬说曰。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拥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矣。地之恶者。则反是。又曰。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亦其理也。又朱子山陵议状。有曰。以子孙而葬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其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愚于此事。固无所见。今但据此程朱二说而言之。父子一气。彼安此安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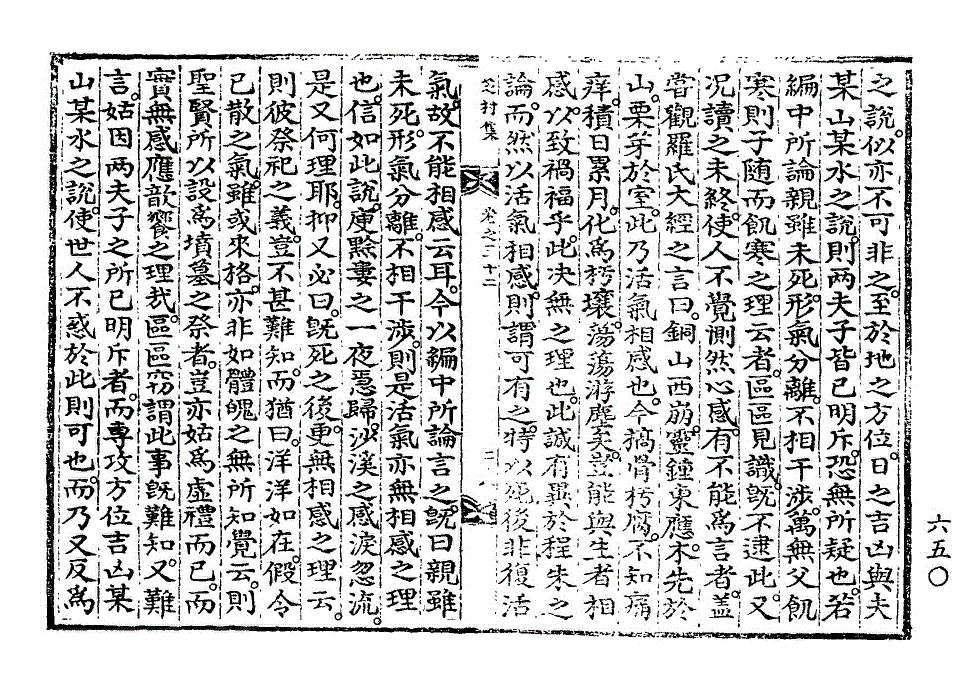 之说。似亦不可非之。至于地之方位。日之吉凶与夫某山某水之说。则两夫子皆已明斥。恐无所疑也。若编中所论亲虽未死。形气分离。不相干涉。万无父饥寒则子随而饥寒之理云者。区区见识。既不逮此。又况读之未终。使人不觉恻然心感。有不能为言者。盖尝观罗氏大经之言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先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槁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此诚有异于程朱之论。而然以活气相感。则谓可有之。特以死后非复活气。故不能相感云耳。今以编中所论言之。既曰亲虽未死。形气分离。不相干涉。则是活气亦无相感之理也。信如此说。庾黔娄之一夜急归。沙溪之感泪忽流。是又何理耶。抑又必曰。既死之后。更无相感之理云。则彼祭祀之义。岂不甚难知。而犹曰。洋洋如在。假令已散之气。虽或来格。亦非如体魄之无所知觉云。则圣贤所以设为坟墓之祭者。岂亦姑为虚礼而已。而实无感应歆飨之理哉。区区窃谓此事既难知。又难言。姑因两夫子之所已明斥者。而专攻方位吉凶某山某水之说。使世人不惑于此则可也。而乃又反为
之说。似亦不可非之。至于地之方位。日之吉凶与夫某山某水之说。则两夫子皆已明斥。恐无所疑也。若编中所论亲虽未死。形气分离。不相干涉。万无父饥寒则子随而饥寒之理云者。区区见识。既不逮此。又况读之未终。使人不觉恻然心感。有不能为言者。盖尝观罗氏大经之言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先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槁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此诚有异于程朱之论。而然以活气相感。则谓可有之。特以死后非复活气。故不能相感云耳。今以编中所论言之。既曰亲虽未死。形气分离。不相干涉。则是活气亦无相感之理也。信如此说。庾黔娄之一夜急归。沙溪之感泪忽流。是又何理耶。抑又必曰。既死之后。更无相感之理云。则彼祭祀之义。岂不甚难知。而犹曰。洋洋如在。假令已散之气。虽或来格。亦非如体魄之无所知觉云。则圣贤所以设为坟墓之祭者。岂亦姑为虚礼而已。而实无感应歆飨之理哉。区区窃谓此事既难知。又难言。姑因两夫子之所已明斥者。而专攻方位吉凶某山某水之说。使世人不惑于此则可也。而乃又反为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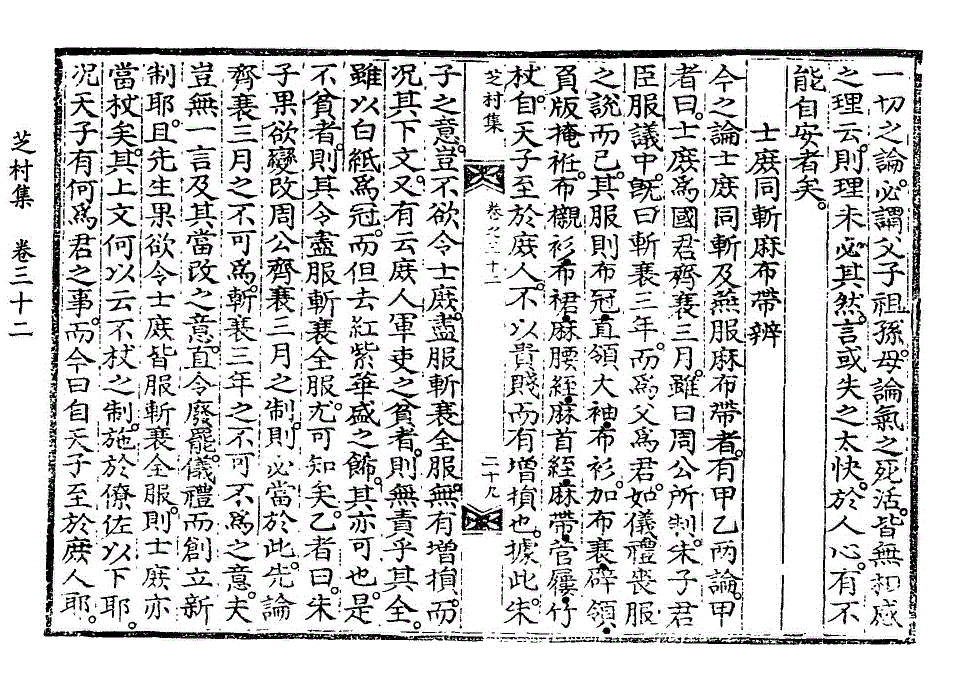 一切之论。必谓父子祖孙。毋论气之死活。皆无相感之理云。则理未必其然。言或失之太快。于人心。有不能自安者矣。
一切之论。必谓父子祖孙。毋论气之死活。皆无相感之理云。则理未必其然。言或失之太快。于人心。有不能自安者矣。士庶同斩麻布带辨
今之论士庶同斩及燕服麻布带者。有甲乙两论。甲者曰。士庶为国君齐衰三月。虽曰周公所制。朱子君臣服议中。既曰斩衰三年。而为父为君。如仪礼丧服之说而已。其服则布冠,直领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领,负版掩衽。布衬衫,布裙,麻腰绖,麻首绖,麻带,菅屦,竹杖。自天子至于庶人。不以贵贱而有增损也。据此。朱子之意。岂不欲令士庶。尽服斩衰全服。无有增损。而况其下文。又有云庶人军吏之贫者。则无责乎其全。虽以白纸为冠。而但去红紫华盛之饰。其亦可也。是不贫者。则其令尽服斩衰全服。尤可知矣。乙者曰。朱子果欲变改周公齐衰三月之制。则必当于此。先论齐衰三月之不可为。斩衰三年之不可不为之意。夫岂无一言及其当改之意。直令废罢。仪礼而创立新制耶。且先生果欲令士庶皆服斩衰全服。则士庶亦当杖矣。其上文何以云不杖之制。施于僚佐以下耶。况天子有何为君之事。而今曰自天子至于庶人耶。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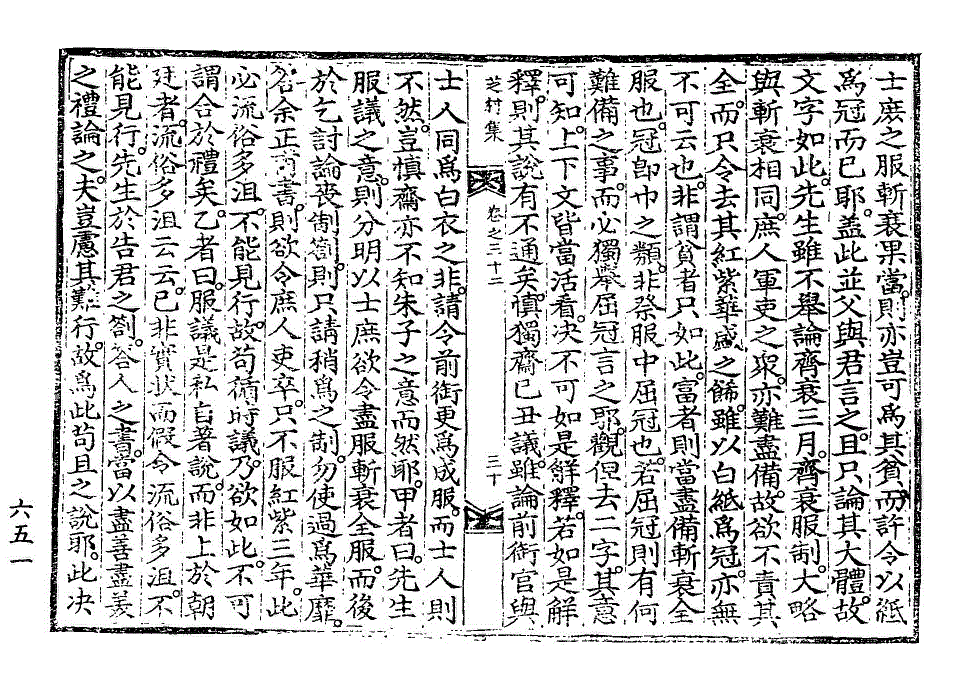 士庶之服斩衰果当。则亦岂可为其贫。而许令以纸为冠而已耶。盖此并父与君言之。且只论其大体。故文字如此。先生虽不举论齐衰三月。齐衰服制。大略与斩衰相同。庶人军吏之众。亦难尽备。故欲不责其全。而只令去其红紫华盛之饰。虽以白纸为冠。亦无不可云也。非谓贫者只如此。富者则当尽备斩衰全服也。冠即巾之类。非祭服中屈冠也。若屈冠则有何难备之事。而必独举屈冠言之耶。观但去二字。其意可知。上下文皆当活看。决不可如是解释。若如是解释。则其说有不通矣。慎独斋己丑议。虽论前衔官与士人同为白衣之非。请令前衔更为成服。而士人则不然。岂慎斋亦不知朱子之意而然耶。甲者曰。先生服议之意。则分明以士庶欲令尽服斩衰全服。而后于乞讨论丧制劄。则只请稍为之制。勿使过为华靡。答余正甫书。则欲令庶人吏卒。只不服红紫三年。此必流俗多沮。不能见行。故苟循时议。乃欲如此。不可谓合于礼矣。乙者曰。服议是私自著说。而非上于朝廷者。流俗多沮云云。已非实状而假令流俗多沮。不能见行。先生于告君之劄。答人之书。当以尽善尽美之礼论之。夫岂虑其难行。故为此苟且之说耶。此决
士庶之服斩衰果当。则亦岂可为其贫。而许令以纸为冠而已耶。盖此并父与君言之。且只论其大体。故文字如此。先生虽不举论齐衰三月。齐衰服制。大略与斩衰相同。庶人军吏之众。亦难尽备。故欲不责其全。而只令去其红紫华盛之饰。虽以白纸为冠。亦无不可云也。非谓贫者只如此。富者则当尽备斩衰全服也。冠即巾之类。非祭服中屈冠也。若屈冠则有何难备之事。而必独举屈冠言之耶。观但去二字。其意可知。上下文皆当活看。决不可如是解释。若如是解释。则其说有不通矣。慎独斋己丑议。虽论前衔官与士人同为白衣之非。请令前衔更为成服。而士人则不然。岂慎斋亦不知朱子之意而然耶。甲者曰。先生服议之意。则分明以士庶欲令尽服斩衰全服。而后于乞讨论丧制劄。则只请稍为之制。勿使过为华靡。答余正甫书。则欲令庶人吏卒。只不服红紫三年。此必流俗多沮。不能见行。故苟循时议。乃欲如此。不可谓合于礼矣。乙者曰。服议是私自著说。而非上于朝廷者。流俗多沮云云。已非实状而假令流俗多沮。不能见行。先生于告君之劄。答人之书。当以尽善尽美之礼论之。夫岂虑其难行。故为此苟且之说耶。此决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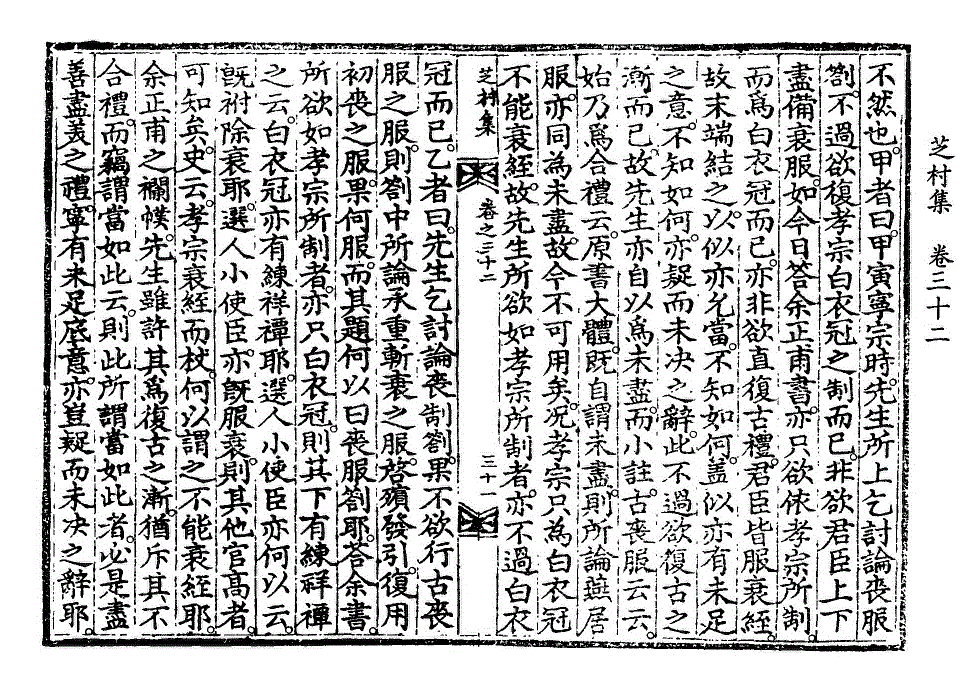 不然也。甲者曰。甲寅宁宗时。先生所上乞讨论丧服劄。不过欲复孝宗白衣冠之制而已。非欲君臣上下尽备衰服。如今日答余正甫书。亦只欲依孝宗所制。而为白衣冠而已。亦非欲直复古礼。君臣皆服衰绖。故末端结之。以似亦允当。不知如何。盖似亦有未足之意。不知如何。亦疑而未决之辞。此不过欲复古之渐而已。故先生亦自以为未尽。而小注。古丧服云云。始乃为合礼云。原书大体。既自谓未尽。则所论燕居服。亦同为未尽。故今不可用矣。况孝宗只为白衣冠不能衰绖。故先生所欲如孝宗所制者。亦不过白衣冠而已。乙者曰。先生乞讨论丧制劄。果不欲行古丧服之服。则劄中所论承重斩衰之服。启殡发引。复用初丧之服。果何服。而其题何以曰丧服劄耶。答余书。所欲如孝宗所制者。亦只白衣冠。则其下有练祥禫之云。白衣冠亦有练祥禫耶。选人小使臣亦何以云。既祔除衰耶。选人小使臣。亦既服衰。则其他官高者。可知矣。史云。孝宗衰绖而杖。何以谓之不能衰绖耶。余正甫之襕幞。先生虽许其为复古之渐。犹斥其不合礼。而窃谓当如此云。则此所谓当如此者。必是尽善尽美之礼。宁有未足底意。亦岂疑而未决之辞耶。
不然也。甲者曰。甲寅宁宗时。先生所上乞讨论丧服劄。不过欲复孝宗白衣冠之制而已。非欲君臣上下尽备衰服。如今日答余正甫书。亦只欲依孝宗所制。而为白衣冠而已。亦非欲直复古礼。君臣皆服衰绖。故末端结之。以似亦允当。不知如何。盖似亦有未足之意。不知如何。亦疑而未决之辞。此不过欲复古之渐而已。故先生亦自以为未尽。而小注。古丧服云云。始乃为合礼云。原书大体。既自谓未尽。则所论燕居服。亦同为未尽。故今不可用矣。况孝宗只为白衣冠不能衰绖。故先生所欲如孝宗所制者。亦不过白衣冠而已。乙者曰。先生乞讨论丧制劄。果不欲行古丧服之服。则劄中所论承重斩衰之服。启殡发引。复用初丧之服。果何服。而其题何以曰丧服劄耶。答余书。所欲如孝宗所制者。亦只白衣冠。则其下有练祥禫之云。白衣冠亦有练祥禫耶。选人小使臣亦何以云。既祔除衰耶。选人小使臣。亦既服衰。则其他官高者。可知矣。史云。孝宗衰绖而杖。何以谓之不能衰绖耶。余正甫之襕幞。先生虽许其为复古之渐。犹斥其不合礼。而窃谓当如此云。则此所谓当如此者。必是尽善尽美之礼。宁有未足底意。亦岂疑而未决之辞耶。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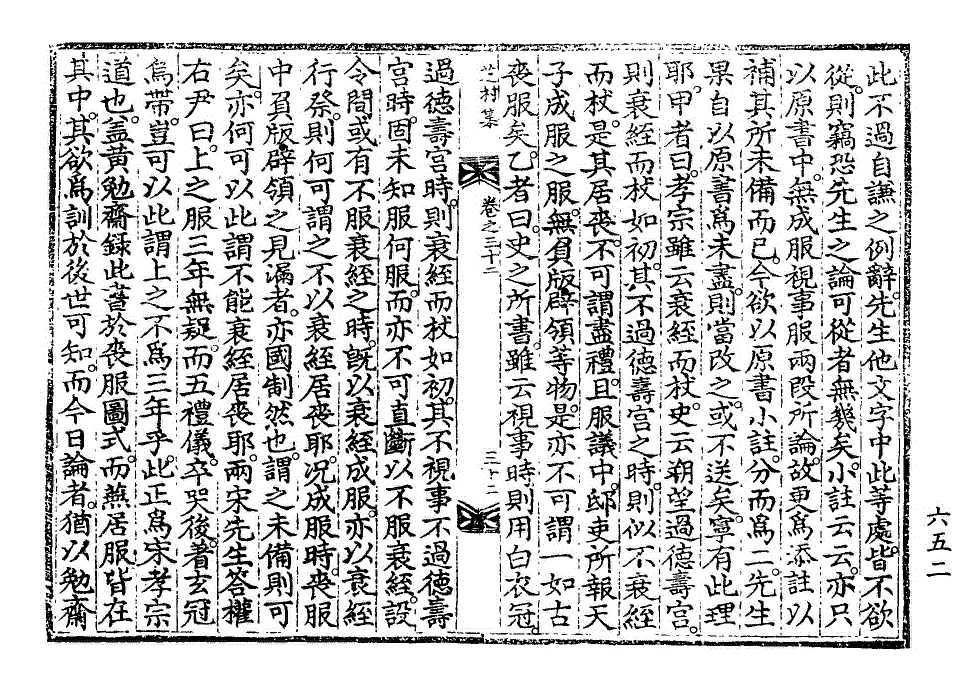 此不过自谦之例辞。先生他文字中此等处。皆不欲从。则窃恐先生之论可从者无几矣。小注云云。亦只以原书中。无成服视事服两段所论。故更为添注以补其所未备而已。今欲以原书小注。分而为二。先生果自以原书为未尽。则当改之。或不送矣。宁有此理耶。甲者曰。孝宗虽云衰绖而杖。史云朔望过德寿宫。则衰绖而杖如初。其不过德寿宫之时。则似不衰绖而杖。是其居丧。不可谓尽礼。且服议中。邸吏所报天子成服之服。无负版,辟领等物。是亦不可谓一如古丧服矣。乙者曰。史之所书。虽云视事时则用白衣冠。过德寿宫时。则衰绖而杖如初。其不视事不过德寿宫时。固未知服何服。而亦不可直断以不服衰绖。设令间或有不服衰绖之时。既以衰绖成服。亦以衰绖行祭。则何可谓之不以衰绖居丧耶。况成服时。丧服中负版,辟领之见漏者。亦国制然也。谓之未备则可矣。亦何可以此谓不能衰绖居丧耶。两宋先生答权右尹曰。上之服三年无疑。而五礼仪。卒哭后。着玄冠乌带。岂可以此谓上之不为三年乎。此正为宋孝宗道也。盖黄勉斋录此书于丧服图式。而燕居服皆在其中。其欲为训于后世可知。而今日论者。犹以勉斋
此不过自谦之例辞。先生他文字中此等处。皆不欲从。则窃恐先生之论可从者无几矣。小注云云。亦只以原书中。无成服视事服两段所论。故更为添注以补其所未备而已。今欲以原书小注。分而为二。先生果自以原书为未尽。则当改之。或不送矣。宁有此理耶。甲者曰。孝宗虽云衰绖而杖。史云朔望过德寿宫。则衰绖而杖如初。其不过德寿宫之时。则似不衰绖而杖。是其居丧。不可谓尽礼。且服议中。邸吏所报天子成服之服。无负版,辟领等物。是亦不可谓一如古丧服矣。乙者曰。史之所书。虽云视事时则用白衣冠。过德寿宫时。则衰绖而杖如初。其不视事不过德寿宫时。固未知服何服。而亦不可直断以不服衰绖。设令间或有不服衰绖之时。既以衰绖成服。亦以衰绖行祭。则何可谓之不以衰绖居丧耶。况成服时。丧服中负版,辟领之见漏者。亦国制然也。谓之未备则可矣。亦何可以此谓不能衰绖居丧耶。两宋先生答权右尹曰。上之服三年无疑。而五礼仪。卒哭后。着玄冠乌带。岂可以此谓上之不为三年乎。此正为宋孝宗道也。盖黄勉斋录此书于丧服图式。而燕居服皆在其中。其欲为训于后世可知。而今日论者。犹以勉斋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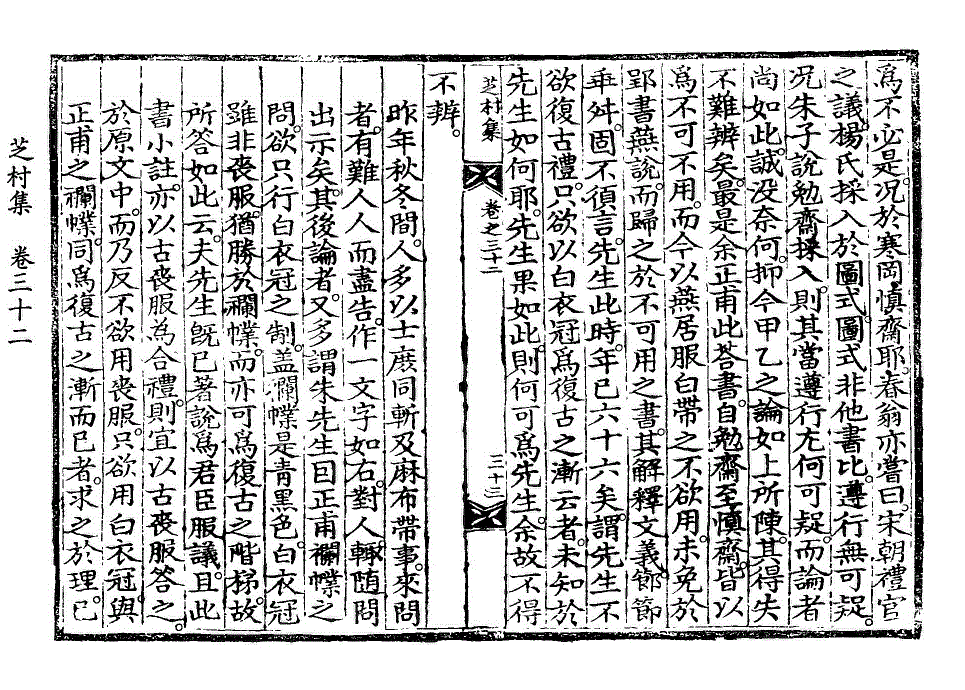 为不必是。况于寒冈,慎斋耶。春翁亦尝曰。宋朝礼官之议。杨氏采入于图式。图式非他书比。遵行无可疑。况朱子说勉斋采入。则其当遵行尤何可疑。而论者尚如此。诚没奈何。抑今甲乙之论如上所陈。其得失不难辨矣。最是余正甫此答书。自勉斋至慎斋。皆以为不可不用。而今以燕居服白带之不欲用。未免于郢书燕说。而归之于不可用之书。其解释文义。节节乖舛。固不须言。先生此时。年已六十六矣。谓先生不欲复古礼。只欲以白衣冠为复古之渐云者。未知于先生如何耶。先生果如此。则何可为先生。余故不得不辨。
为不必是。况于寒冈,慎斋耶。春翁亦尝曰。宋朝礼官之议。杨氏采入于图式。图式非他书比。遵行无可疑。况朱子说勉斋采入。则其当遵行尤何可疑。而论者尚如此。诚没奈何。抑今甲乙之论如上所陈。其得失不难辨矣。最是余正甫此答书。自勉斋至慎斋。皆以为不可不用。而今以燕居服白带之不欲用。未免于郢书燕说。而归之于不可用之书。其解释文义。节节乖舛。固不须言。先生此时。年已六十六矣。谓先生不欲复古礼。只欲以白衣冠为复古之渐云者。未知于先生如何耶。先生果如此。则何可为先生。余故不得不辨。昨年秋冬间。人多以士庶同斩及麻布带事。来问者。有难人人而尽告。作一文字如右。对人。辄随问出示矣。其后论者。又多谓朱先生因正甫襕幞之问。欲只行白衣冠之制。盖襕幞是青黑色。白衣冠虽非丧服。犹胜于襕幞。而亦可为复古之阶梯。故所答如此云。夫先生既已著说为君臣服议。且此书小注。亦以古丧服为合礼。则宜以古丧服答之。于原文中。而乃反不欲用丧服。只欲用白衣冠。与正甫之襕幞。同为复古之渐而已者。求之于理。已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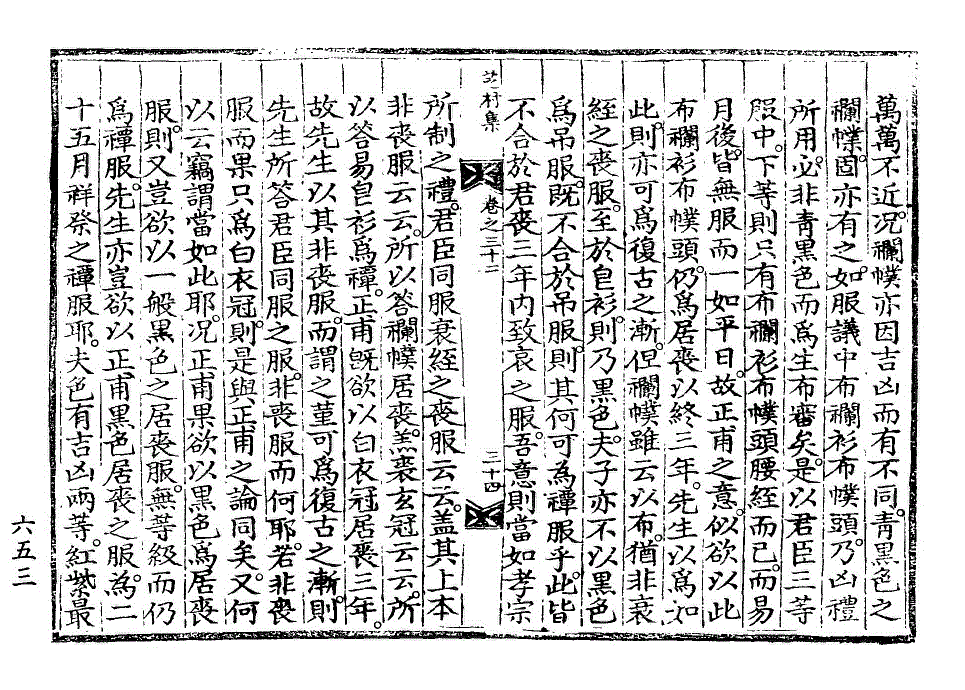 万万不近。况襕幞亦因吉凶而有不同。青黑色之襕幞。固亦有之。如服议中布襕衫布幞头。乃凶礼所用。必非青黑色而为生布审矣。是以君臣三等服中。下等则只有布襕衫布幞头腰绖而已。而易月后。皆无服而一如平日。故正甫之意。似欲以此布襕衫布幞头。仍为居丧以终三年。先生以为如此。则亦可为复古之渐。但襕幞虽云以布。犹非衰绖之丧服。至于皂衫。则乃黑色。夫子亦不以黑色为吊服。既不合于吊服。则其何可为禫服乎。此皆不合于君丧三年内致哀之服。吾意则当如孝宗所制之礼。君臣同服衰绖之丧服云云。盖其上本非丧服云云。所以答襕幞居丧。羔裘玄冠云云。所以答易皂衫为禫。正甫既欲以白衣冠居丧三年。故先生以其非丧服。而谓之堇可为复古之渐。则先生所答君臣同服之服。非丧服而何耶。若非丧服而果只为白衣冠。则是与正甫之论同矣。又何以云窃谓当如此耶。况正甫果欲以黑色为居丧服。则又岂欲以一般黑色之居丧服。无等级而仍为禫服。先生亦岂欲以正甫黑色居丧之服。为二十五月祥祭之禫服耶。夫色有吉凶两等。红紫最
万万不近。况襕幞亦因吉凶而有不同。青黑色之襕幞。固亦有之。如服议中布襕衫布幞头。乃凶礼所用。必非青黑色而为生布审矣。是以君臣三等服中。下等则只有布襕衫布幞头腰绖而已。而易月后。皆无服而一如平日。故正甫之意。似欲以此布襕衫布幞头。仍为居丧以终三年。先生以为如此。则亦可为复古之渐。但襕幞虽云以布。犹非衰绖之丧服。至于皂衫。则乃黑色。夫子亦不以黑色为吊服。既不合于吊服。则其何可为禫服乎。此皆不合于君丧三年内致哀之服。吾意则当如孝宗所制之礼。君臣同服衰绖之丧服云云。盖其上本非丧服云云。所以答襕幞居丧。羔裘玄冠云云。所以答易皂衫为禫。正甫既欲以白衣冠居丧三年。故先生以其非丧服。而谓之堇可为复古之渐。则先生所答君臣同服之服。非丧服而何耶。若非丧服而果只为白衣冠。则是与正甫之论同矣。又何以云窃谓当如此耶。况正甫果欲以黑色为居丧服。则又岂欲以一般黑色之居丧服。无等级而仍为禫服。先生亦岂欲以正甫黑色居丧之服。为二十五月祥祭之禫服耶。夫色有吉凶两等。红紫最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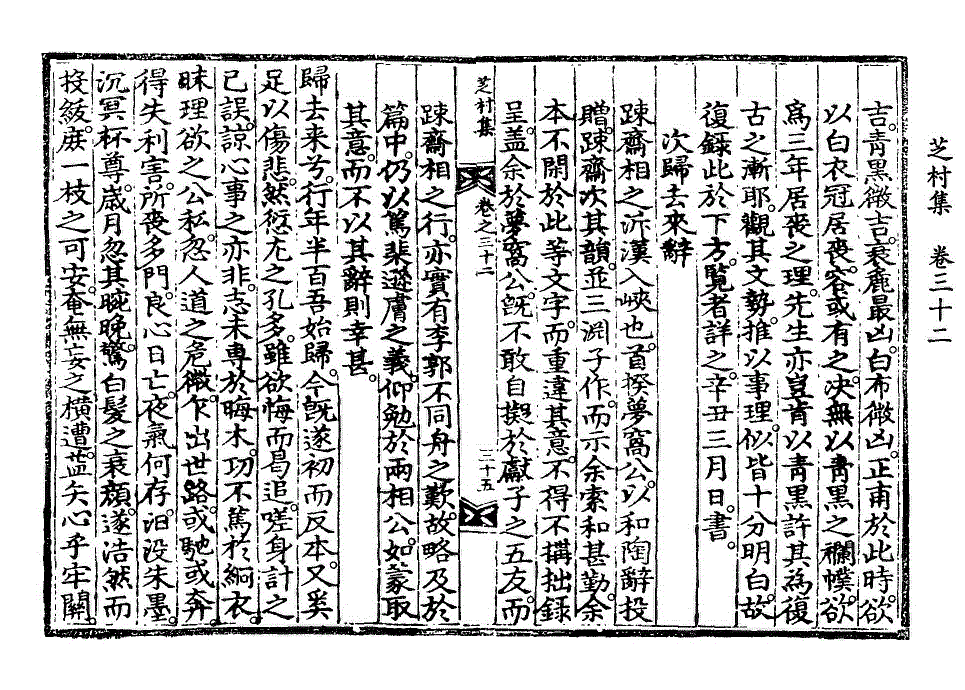 吉。青黑微吉。衰粗最凶。白布微凶。正甫于此时。欲以白衣冠居丧。容或有之。决无以青黑之襕幞。欲为三年居丧之理。先生亦岂肯以青黑许其为复古之渐耶。观其文势。推以事理。似皆十分明白。故复录此于下方。览者详之。辛丑三月日。书。
吉。青黑微吉。衰粗最凶。白布微凶。正甫于此时。欲以白衣冠居丧。容或有之。决无以青黑之襕幞。欲为三年居丧之理。先生亦岂肯以青黑许其为复古之渐耶。观其文势。推以事理。似皆十分明白。故复录此于下方。览者详之。辛丑三月日。书。次归去来辞
疏斋相之溯汉入峡也。首揆梦窝公。以和陶辞投赠。疏斋次其韵。并三渊子作。而示余索和甚勤。余本不闲于此等文字。而重违其意。不得不搆拙录呈。盖余于梦窝公。既不敢自拟于献子之五友。而疏斋相之行。亦实有李郭不同舟之叹。故略及于篇中。仍以笃棐逊肤之义。仰勉于两相公。如蒙取其意。而不以其辞则幸甚。
归去来兮。行年半百吾始归。今既遂初而反本。又奚足以伤悲。然愆尤之孔多。虽欲悔而曷追。嗟身计之已误。谅心事之亦非。志未专于晦木。功不笃于絅衣。昧理欲之公私。忽人道之危微。乍出世路。或驰或奔。得失利害。所丧多门。良心日亡。夜气何存。汩没朱墨。沉冥杯尊。岁月忽其晼晚。惊白发之衰颜。遂浩然而投绂。庶一枝之可安。奄无妄之横遭。益矢心乎牢关。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6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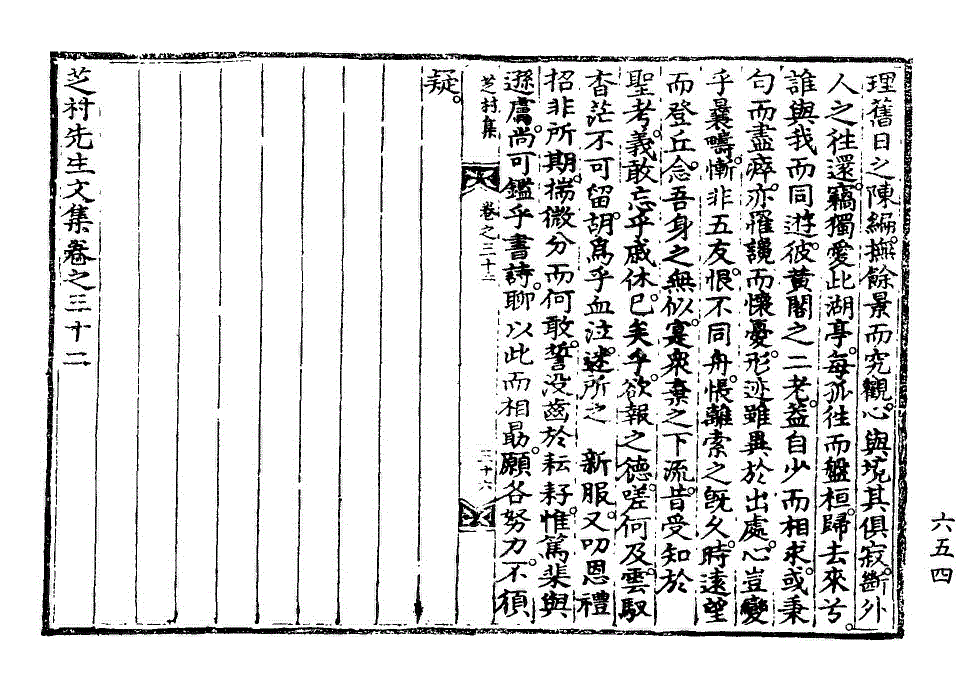 理旧日之陈编。抚馀景而究观。心与境其俱寂。断外人之往还。窃独爱此湖亭。每孤往而盘桓。归去来兮。谁与我而同游。彼黄阁之二老。盖自少而相求。或秉匀而尽瘁。亦罹谗而怀忧。形迹虽异于出处。心岂变乎曩畴。惭非五友。恨不同舟。怅离索之既久。时远望而登丘。念吾身之无似。寔众弃之下流。昔受知于 圣考。义敢忘乎戚休。已矣乎。欲报之德。嗟何及。云驭杳茫不可留。胡为乎血泣。迷所之 新服。又叨恩礼招非所期。揣微分而何敢。誓没齿于耘耔。惟笃棐与逊肤。尚可鉴乎书诗。聊以此而相勖。愿各努力。不须疑。
理旧日之陈编。抚馀景而究观。心与境其俱寂。断外人之往还。窃独爱此湖亭。每孤往而盘桓。归去来兮。谁与我而同游。彼黄阁之二老。盖自少而相求。或秉匀而尽瘁。亦罹谗而怀忧。形迹虽异于出处。心岂变乎曩畴。惭非五友。恨不同舟。怅离索之既久。时远望而登丘。念吾身之无似。寔众弃之下流。昔受知于 圣考。义敢忘乎戚休。已矣乎。欲报之德。嗟何及。云驭杳茫不可留。胡为乎血泣。迷所之 新服。又叨恩礼招非所期。揣微分而何敢。誓没齿于耘耔。惟笃棐与逊肤。尚可鉴乎书诗。聊以此而相勖。愿各努力。不须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