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x 页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劄记
劄记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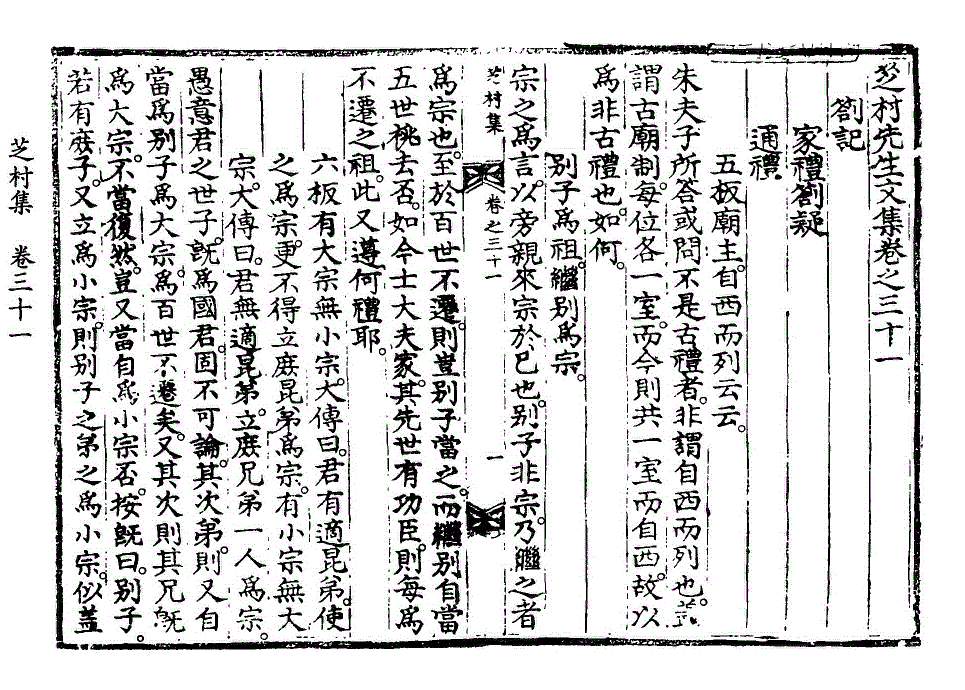 家礼劄疑○通礼
家礼劄疑○通礼五板庙主。自西而列云云。
朱夫子所答或问不是古礼者。非谓自西而列也。盖谓古庙制。每位各一室。而今则共一室而自西。故以为非古礼也。如何。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
宗之为言。以旁亲来宗于己也。别子非宗。乃继之者为宗也。至于百世不迁。则岂别子当之。而继别自当五世祧去否。如今士大夫家。其先世有功臣。则每为不迁之祖。此又遵何礼耶。
六板有大宗无小宗。大传曰。君有适昆弟。使之为宗。更不得立庶昆弟为宗。有小宗无大宗。大传曰。君无适昆弟。立庶兄弟一人为宗。
愚意君之世子。既为国君。固不可论。其次弟。则又自当为别子为大宗。为百世不迁矣。又其次则其兄既为大宗。不当复然。岂又当自为小宗否。按既曰。别子。若有庶子。又立为小宗。则别子之弟之为小宗。似盖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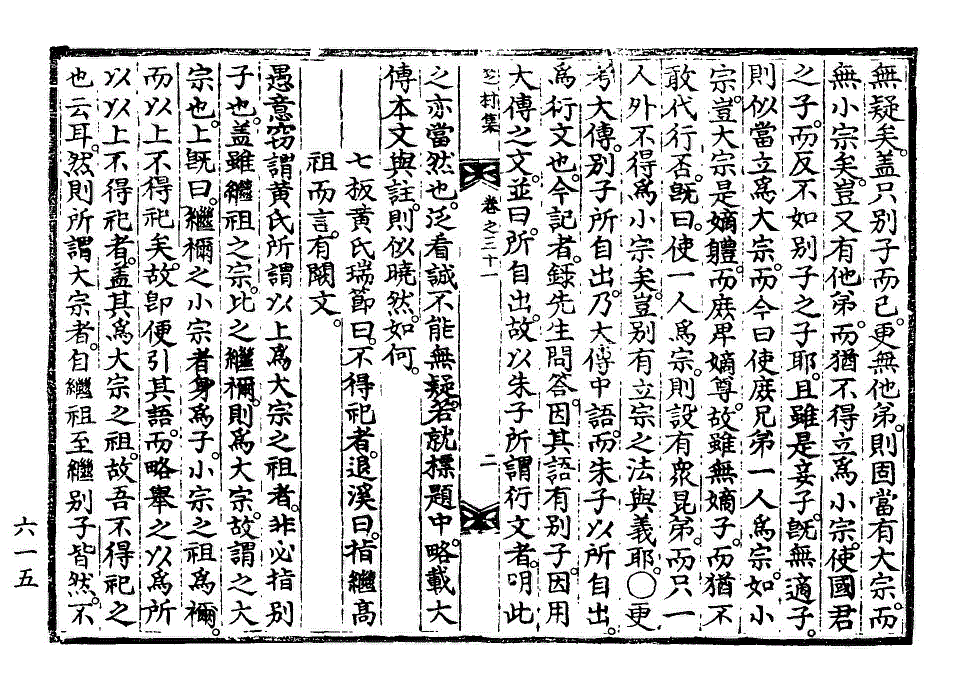 无疑矣。盖只别子而已。更无他弟。则固当有大宗。而无小宗矣。岂又有他弟。而犹不得立为小宗。使国君之子。而反不如别子之子耶。且虽是妾子。既无适子。则似当立为大宗。而今曰使庶兄弟一人为宗。如小宗。岂大宗是嫡体。而庶卑嫡尊。故虽无嫡子。而犹不敢代行否。既曰。使一人为宗。则设有众昆弟。而只一人外不得为小宗矣。岂别有立宗之法与义耶。○更考大传。别子所自出。乃大传中语。而朱子以所自出。为衍文也。今记者。录先生问答。因其语有别子。因用大传之文。并曰。所自出。故以朱子所谓衍文者。明此之亦当然也。泛看诚不能无疑。若就标题中。略载大传本文与注。则似晓然。如何。
无疑矣。盖只别子而已。更无他弟。则固当有大宗。而无小宗矣。岂又有他弟。而犹不得立为小宗。使国君之子。而反不如别子之子耶。且虽是妾子。既无适子。则似当立为大宗。而今曰使庶兄弟一人为宗。如小宗。岂大宗是嫡体。而庶卑嫡尊。故虽无嫡子。而犹不敢代行否。既曰。使一人为宗。则设有众昆弟。而只一人外不得为小宗矣。岂别有立宗之法与义耶。○更考大传。别子所自出。乃大传中语。而朱子以所自出。为衍文也。今记者。录先生问答。因其语有别子。因用大传之文。并曰。所自出。故以朱子所谓衍文者。明此之亦当然也。泛看诚不能无疑。若就标题中。略载大传本文与注。则似晓然。如何。七板黄氏瑞节曰。不得祀者。退溪曰。指继高祖而言。有阙文。
愚意窃谓黄氏所谓以上为大宗之祖者。非必指别子也。盖虽继祖之宗。比之继祢。则为大宗。故谓之大宗也。上既曰。继祢之小宗者身为子。小宗之祖为祢。而以上不得祀矣。故即便引其语。而略举之以为所以以上不得祀者。盖其为大宗之祖。故吾不得祀之也云耳。然则所谓大宗者。自继祖至继别子皆然。不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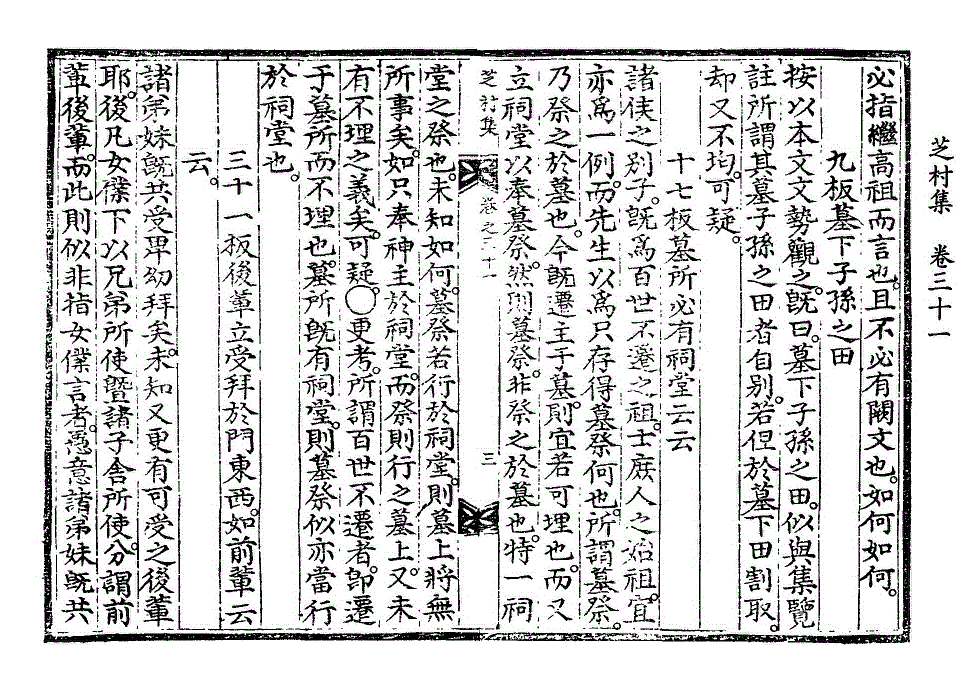 必指继高祖而言也。且不必有阙文也。如何如何。
必指继高祖而言也。且不必有阙文也。如何如何。九板墓下子孙之田
按以本文文势观之。既曰。墓下子孙之田。似与集览注所谓其墓子孙之田者自别。若但于墓下田割取。却又不均。可疑。
十七板墓所必有祠堂云云
诸侯之别子。既为百世不迁之祖。士庶人之始祖。宜亦为一例。而先生以为只存得墓祭何也。所谓墓祭。乃祭之于墓也。今既迁主于墓。则宜若可埋也。而又立祠堂以奉墓祭。然则墓祭。非祭之于墓也。特一祠堂之祭也。未知如何。墓祭若行于祠堂。则墓上将无所事矣。如只奉神主于祠堂。而祭则行之墓上。又未有不埋之义矣。可疑。○更考。所谓百世不迁者。即迁于墓所而不埋也。墓所既有祠堂。则墓祭似亦当行于祠堂也。
三十一板后辈立受拜于门东西。如前辈云云。
诸弟妹既共受卑幼拜矣。未知又更有可受之后辈耶。后凡女仆下以兄弟所使暨诸子舍所使。分谓前辈后辈。而此则似非指女仆言者。愚意诸弟妹既共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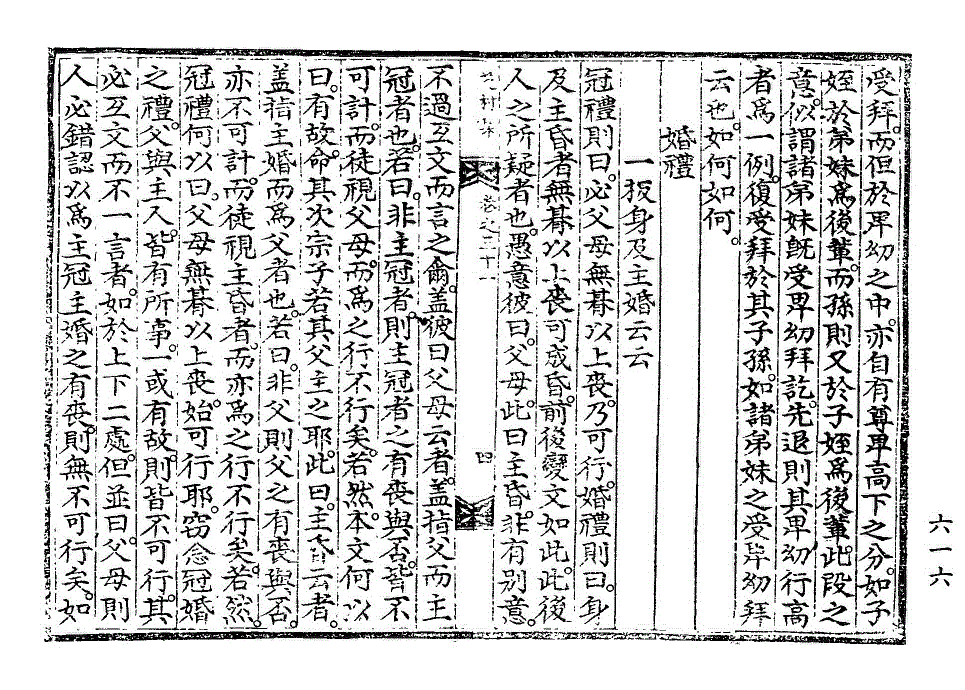 受拜。而但于卑幼之中。亦自有尊卑高下之分。如子侄于弟妹为后辈。而孙则又于子侄为后辈。此段之意。似谓诸弟妹既受卑幼拜讫。先退则其卑幼行高者为一例。复受拜于其子孙。如诸弟妹之受卑幼拜云也。如何如何。
受拜。而但于卑幼之中。亦自有尊卑高下之分。如子侄于弟妹为后辈。而孙则又于子侄为后辈。此段之意。似谓诸弟妹既受卑幼拜讫。先退则其卑幼行高者为一例。复受拜于其子孙。如诸弟妹之受卑幼拜云也。如何如何。家礼劄疑O婚礼
一板身及主婚云云
冠礼则曰。必父母无期以上丧。乃可行。婚礼则曰。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可成昏。前后变文如此。此后人之所疑者也。愚意彼曰。父母。此曰主昏。非有别意。不过互文而言之尔。盖彼曰父母云者。盖指父而主冠者也。若曰。非主冠者。则主冠者之有丧与否。皆不可计。而徒视父母。而为之行不行矣。若然。本文何以曰。有故。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耶。此曰。主昏云者。盖指主婚而为父者也。若曰。非父则父之有丧与否。亦不可计。而徒视主昏者。而亦为之行不行矣。若然。冠礼何以曰。父母无期以上丧。始可行耶。窃念冠婚之礼。父与主人。皆有所事。一或有故。则皆不可行。其必互文而不一言者。如于上下二处。但并曰。父母则人必错认以为主冠主婚之有丧。则无不可行矣。如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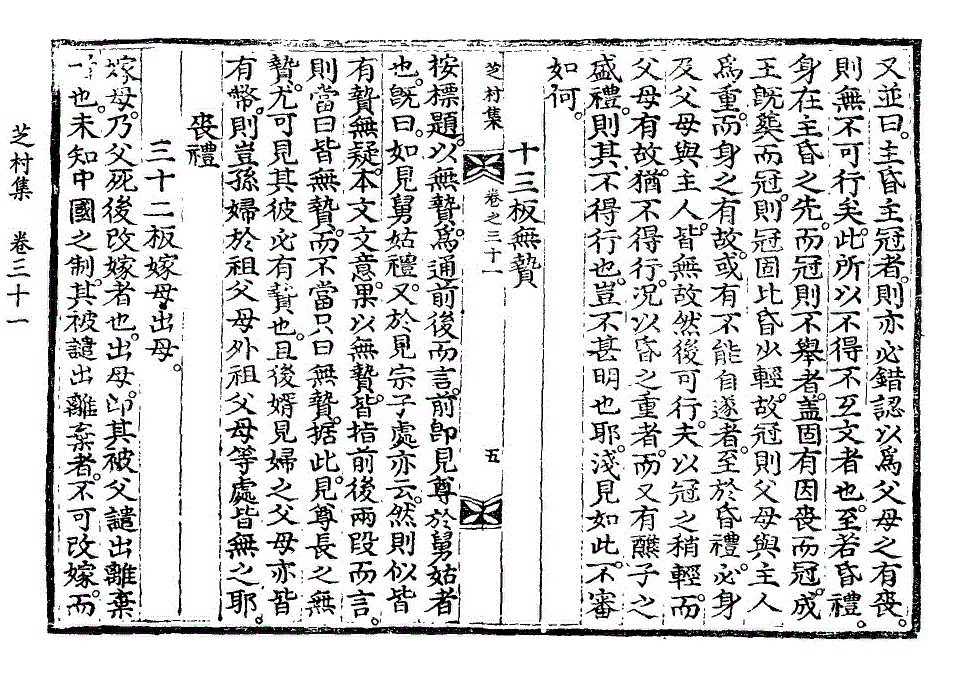 又并曰。主昏主冠者。则亦必错认以为父母之有丧。则无不可行矣。此所以不得不互文者也。至若昏礼。身在主昏之先。而冠则不举者。盖固有因丧而冠。成王既葬而冠。则冠固比昏少轻。故冠则父母与主人为重。而身之有故。或有不能自遂者。至于昏礼。必身及父母与主人。皆无故然后可行。夫以冠之稍轻。而父母有故。犹不得行。况以昏之重者。而又有醮子之盛礼。则其不得行也。岂不甚明也耶。浅见如此。不审如何。
又并曰。主昏主冠者。则亦必错认以为父母之有丧。则无不可行矣。此所以不得不互文者也。至若昏礼。身在主昏之先。而冠则不举者。盖固有因丧而冠。成王既葬而冠。则冠固比昏少轻。故冠则父母与主人为重。而身之有故。或有不能自遂者。至于昏礼。必身及父母与主人。皆无故然后可行。夫以冠之稍轻。而父母有故。犹不得行。况以昏之重者。而又有醮子之盛礼。则其不得行也。岂不甚明也耶。浅见如此。不审如何。十三板无贽
按标题。以无贽。为通前后而言。前即见尊于舅姑者也。既曰。如见舅姑礼。又于见宗子处亦云。然则似皆有贽无疑。本文文意。果以无贽。皆指前后两段而言。则当曰皆无贽。而不当只曰无贽。据此。见尊长之无贽。尤可见其彼必有贽也。且后婿见妇之父母亦皆有币。则岂孙妇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处皆无之耶。
家礼劄疑O丧礼
三十二板嫁母,出母。
嫁母。乃父死后改嫁者也。出母。即其被父谴出离弃者也。未知中国之制。其被谴出离弃者。不可改嫁。而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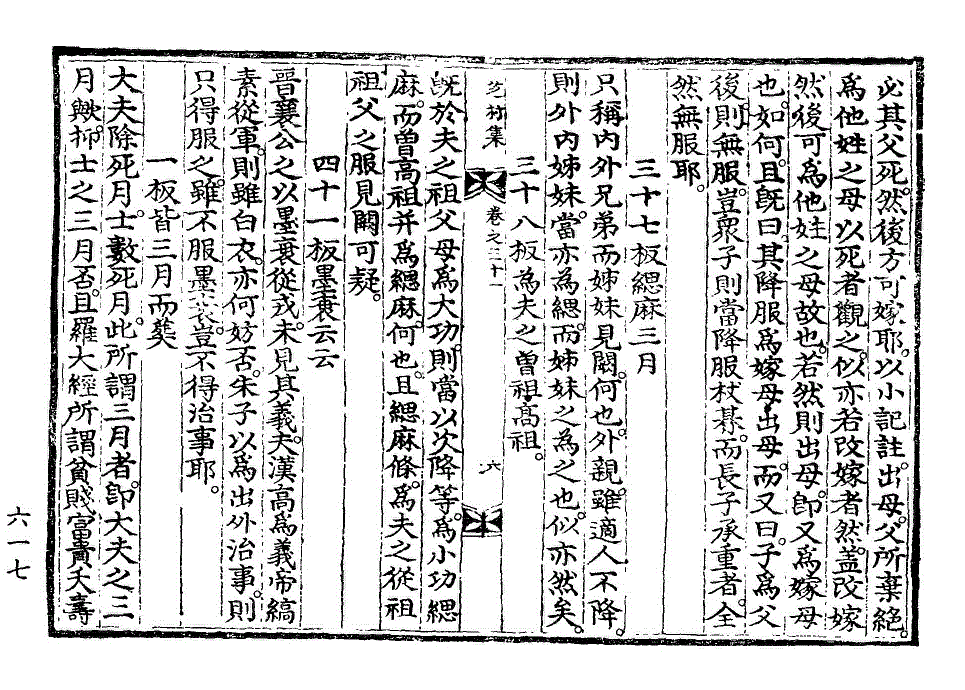 必其父死。然后方可嫁耶。以小记注。出母。父所弃绝。为他姓之母以死者观之。似亦若改嫁者然。盖改嫁然后可为他姓之母故也。若然则出母。即又为嫁母也。如何。且既曰。其降服为嫁母,出母。而又曰。子为父后。则无服。岂众子则当降服杖期。而长子承重者。全然无服耶。
必其父死。然后方可嫁耶。以小记注。出母。父所弃绝。为他姓之母以死者观之。似亦若改嫁者然。盖改嫁然后可为他姓之母故也。若然则出母。即又为嫁母也。如何。且既曰。其降服为嫁母,出母。而又曰。子为父后。则无服。岂众子则当降服杖期。而长子承重者。全然无服耶。三十七板缌麻三月
只称内外兄弟而姊妹见阙。何也。外亲。虽适人不降。则外内姊妹。当亦为缌。而姊妹之为之也。似亦然矣。
三十八板为夫之曾祖,高祖。
既于夫之祖父母为大功。则当以次降等。为小功缌麻。而曾高祖并为缌麻。何也。且缌麻条。为夫之从祖祖父之服见阙可疑。
四十一板墨衰云云
晋襄公之以墨衰从戎。未见其义。夫汉高为义帝缟素从军。则虽白衣。亦何妨否。朱子以为出外治事。则只得服之。虽不服墨衰。岂不得治事耶。
一板皆三月而葬
大夫除死月。士数死月。此所谓三月者。即大夫之三月欤。抑士之三月否。且罗大经所谓贫贱富贵夭寿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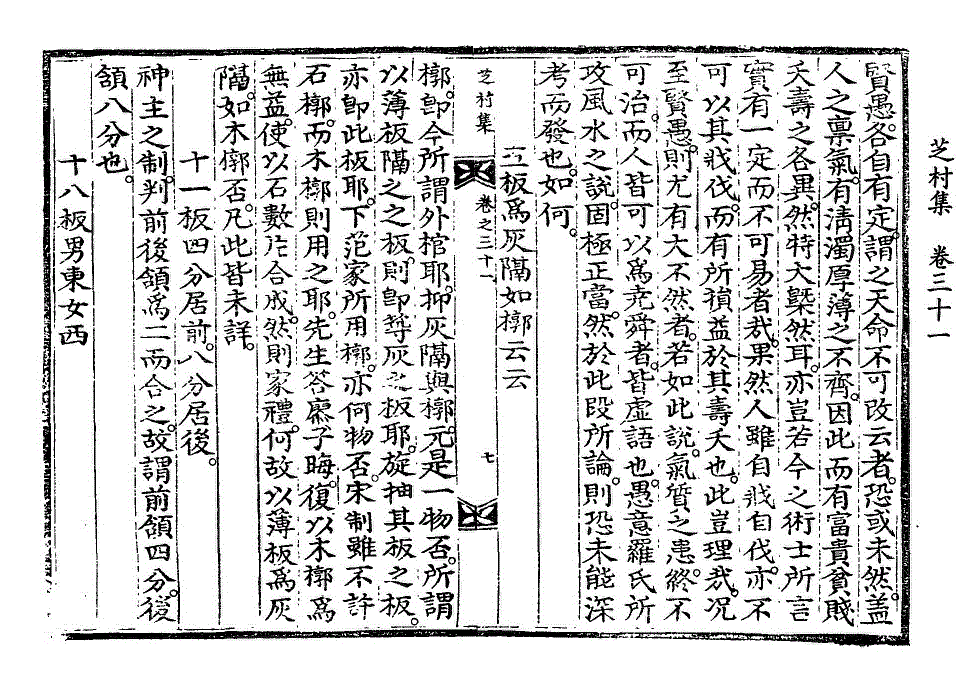 贤愚。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云者。恐或未然。盖人之禀气。有清浊厚薄之不齐。因此而有富贵贫贱夭寿之各异。然特大槩然耳。亦岂若今之术士所言实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哉。果然人虽自戕自伐。亦不可以其戕伐。而有所损益于其寿夭也。此岂理哉。况至贤愚。则尤有大不然者。若如此说。气质之患。终不可治。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皆虚语也。愚意罗氏所攻风水之说。固极正当。然于此段所论。则恐未能深考而发也。如何。
贤愚。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云者。恐或未然。盖人之禀气。有清浊厚薄之不齐。因此而有富贵贫贱夭寿之各异。然特大槩然耳。亦岂若今之术士所言实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哉。果然人虽自戕自伐。亦不可以其戕伐。而有所损益于其寿夭也。此岂理哉。况至贤愚。则尤有大不然者。若如此说。气质之患。终不可治。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皆虚语也。愚意罗氏所攻风水之说。固极正当。然于此段所论。则恐未能深考而发也。如何。五板为灰隔如椁云云
椁。即今所谓外棺耶。抑灰隔与椁。元是一物否。所谓以薄板隔之之板。则即筑灰之板耶。旋抽其板之板。亦即此板耶。下范家所用椁。亦何物否。宋制虽不许石椁。而木椁则用之耶。先生答廖子晦。复以木椁为无益。使以石数片合成。然则家礼。何故以薄板为灰隔。如木椁否。凡此皆未详。
十一板四分居前。八分居后。
神主之制。判前后颔为二而合之。故谓前颔四分。后颔八分也。
十八板男东女西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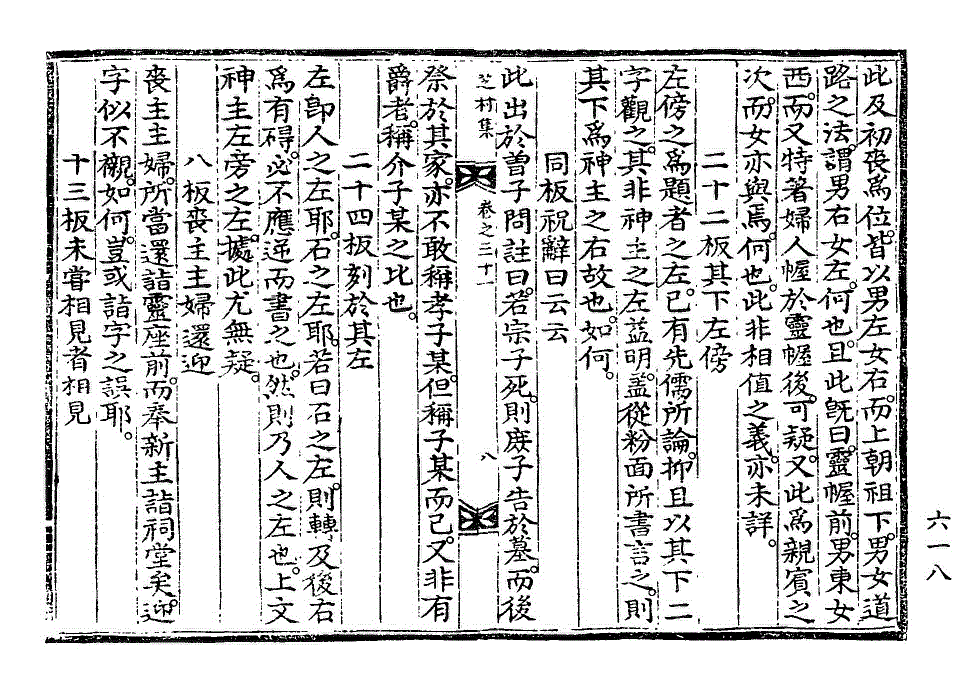 此及初丧为位。皆以男左女右。而上朝祖下。男女道路之法。谓男右女左。何也。且此既曰。灵幄前。男东女西。而又特著妇人幄于灵幄后。可疑。又此为亲宾之次。而女亦与焉。何也。此非相值之义。亦未详。
此及初丧为位。皆以男左女右。而上朝祖下。男女道路之法。谓男右女左。何也。且此既曰。灵幄前。男东女西。而又特著妇人幄于灵幄后。可疑。又此为亲宾之次。而女亦与焉。何也。此非相值之义。亦未详。二十二板其下左傍
左傍之为题者之左。已有先儒所论。抑且以其下二字观之。其非神主之左益明。盖从粉面所书言之。则其下为神主之右故也。如何。
同板祝辞曰云云
此出于曾子问注曰。若宗子死。则庶子告于墓。而后祭于其家。亦不敢称孝子某。但称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称介子某之比也。
二十四板刻于其左
左即人之左耶。石之左耶。若曰石之左。则转及后右为有碍。必不应逆而书之也。然则乃人之左也。上文神主左旁之左。据此尤无疑。
八板丧主主妇还迎
丧主主妇。所当还诣灵座前。而奉新主诣祠堂矣。迎字似不衬。如何。岂或诣字之误耶。
十三板未尝相见者相见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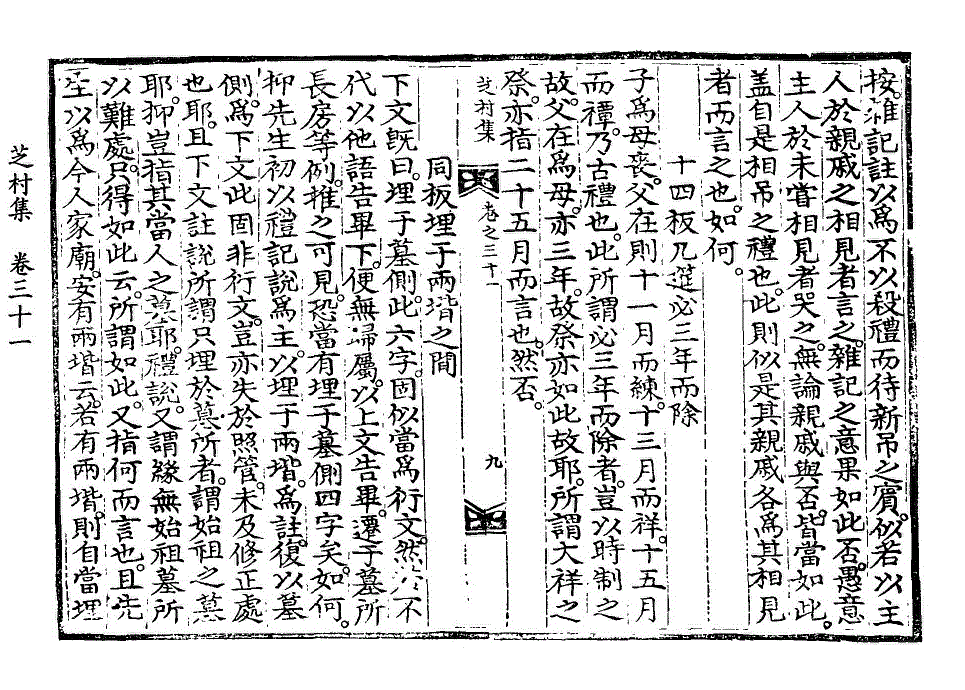 按。杂记注以为不以杀礼而待新吊之宾。似若以主人于亲戚之相见者言之。杂记之意果如此否。愚意主人于未尝相见者哭之。无论亲戚与否。皆当如此。盖自是相吊之礼也。此则似是其亲戚各为其相见者而言之也。如何。
按。杂记注以为不以杀礼而待新吊之宾。似若以主人于亲戚之相见者言之。杂记之意果如此否。愚意主人于未尝相见者哭之。无论亲戚与否。皆当如此。盖自是相吊之礼也。此则似是其亲戚各为其相见者而言之也。如何。十四板几筵必三年而除
子为母丧。父在则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乃古礼也。此所谓必三年而除者。岂以时制之故。父在为母。亦三年。故祭亦如此故耶。所谓大祥之祭。亦指二十五月而言也。然否。
同板埋于两阶之间
下文既曰。埋于墓侧。此六字。固似当为衍文。然若不代以他语告毕下。便无归属。以上文告毕。迁于墓所长房等例。推之可见。恐当有埋于墓侧四字矣。如何。抑先生初以礼记说为主。以埋于两阶。为注。复以墓侧。为下文此固非衍文。岂亦失于照管。未及修正处也耶。且下文注说所谓只埋于墓所者。谓始祖之墓耶。抑岂指其当人之墓耶。礼说。又谓缘无始祖墓所以难处。只得如此云。所谓如此。又指何而言也。且先生以为今人家庙。安有两阶云。若有两阶。则自当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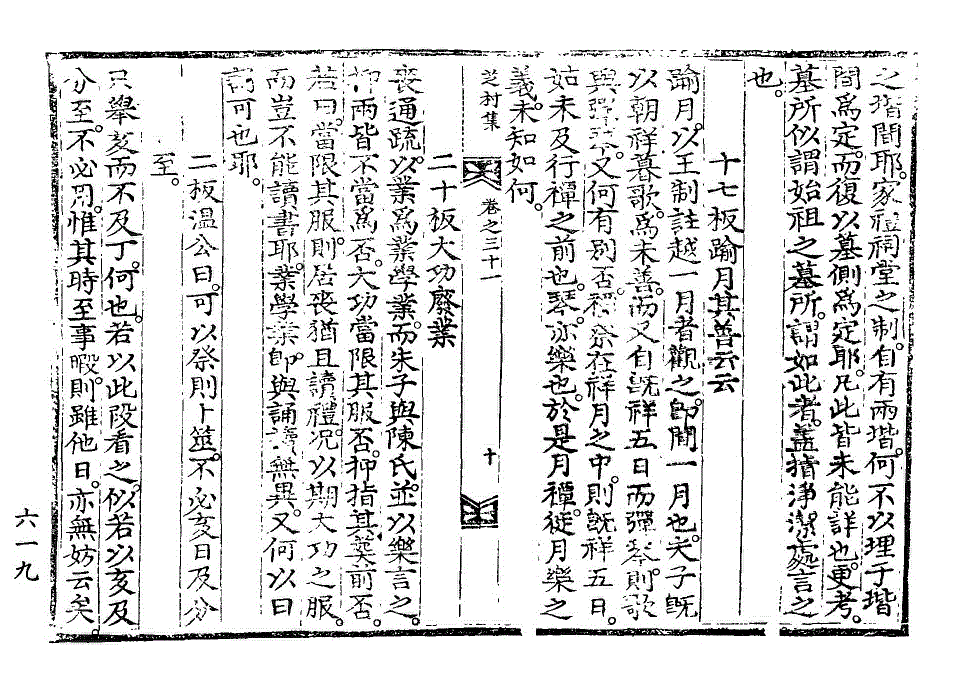 之阶间耶。家礼祠堂之制。自有两阶。何不以埋于阶间为定。而复以墓侧为定耶。凡此皆未能详也。更考。墓所似谓始祖之墓所。谓如此者。盖指净洁处言之也。
之阶间耶。家礼祠堂之制。自有两阶。何不以埋于阶间为定。而复以墓侧为定耶。凡此皆未能详也。更考。墓所似谓始祖之墓所。谓如此者。盖指净洁处言之也。十七板踰月其善云云
踰月。以王制注越一月者观之。即间一月也。夫子既以朝祥暮歌。为未善。而又自既祥五日而弹琴。则歌与弹琴。又何有别否。禫祭在祥月之中。则既祥五日。姑未及行禫之前也。琴。亦乐也。于是月禫。徙月乐之义。未知如何。
二十板大功废业
丧通疏。以业为业学业。而朱子与陈氏。并以乐言之。抑两皆不当为否。大功当限其服否。抑指其葬前否。若曰。当限其服。则居丧犹且读礼。况以期大功之服。而岂不能读书耶。业学业。即与诵读无异。又何以曰诵可也耶。
二板温公曰。可以祭则卜筮。不必亥日及分至。
只举亥而不及丁。何也。若以此段看之。似若以亥及分至。不必用。惟其时至事暇。则虽他日。亦无妨云矣。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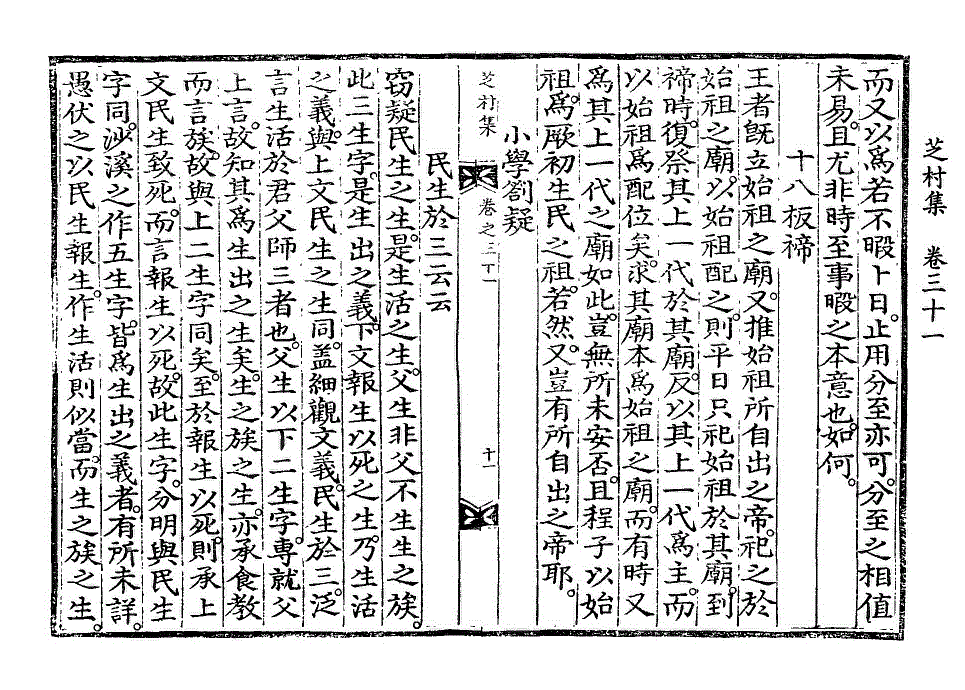 而又以为若不暇卜日。止用分至亦可。分至之相值未易。且尤非时至事暇之本意也。如何。
而又以为若不暇卜日。止用分至亦可。分至之相值未易。且尤非时至事暇之本意也。如何。十八板禘
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以始祖配之。则平日只祀始祖于其庙。到禘时。复祭其上一代于其庙。反以其上一代为主。而以始祖为配位矣。求其庙本为始祖之庙。而有时又为其上一代之庙如此。岂无所未安否。且程子以始祖。为厥初生民之祖。若然。又岂有所自出之帝耶。
小学劄疑
民生于三云云
窃疑民生之生。是生活之生。父生非父不生生之族。此三生字。是生出之义。下文报生以死之生。乃生活之义。与上文民生之生同。盖细观文义。民生于三。泛言生活于君父师三者也。父生以下二生字。专就父上言。故知其为生出之生矣。生之族之生。亦承食教而言族。故与上二生字同矣。至于报生以死。则承上文民生致死。而言报生以死。故此生字。分明与民生字同。沙溪之作五生字。皆为生出之义者。有所未详。愚伏之以民生报生。作生活则似当。而生之族之生。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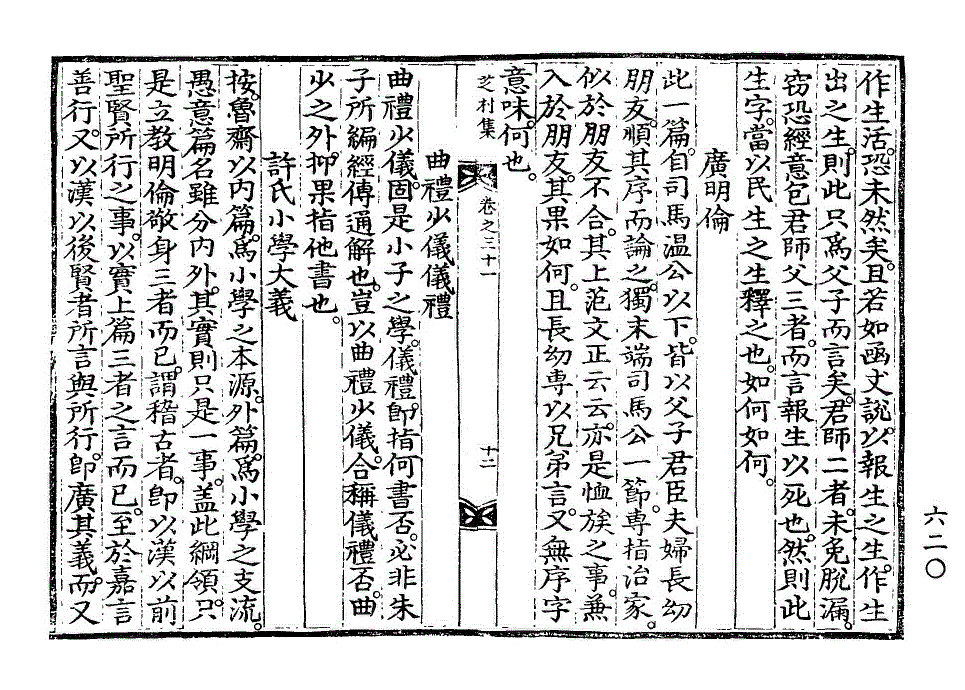 作生活。恐未然矣。且若如函丈说。以报生之生。作生出之生。则此只为父子而言矣。君师二者。未免脱漏。窃恐经意包君师父三者。而言报生以死也。然则此生字。当以民生之生释之也。如何如何。
作生活。恐未然矣。且若如函丈说。以报生之生。作生出之生。则此只为父子而言矣。君师二者。未免脱漏。窃恐经意包君师父三者。而言报生以死也。然则此生字。当以民生之生释之也。如何如何。广明伦
此一篇。自司马温公以下。皆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顺其序而论之。独末端司马公一节。专指治家。似于朋友不合。其上范文正云云。亦是恤族之事。兼入于朋友。其果如何。且长幼专以兄弟言。又无序字意味。何也。
曲礼少仪仪礼
曲礼少仪。固是小子之学。仪礼。即指何书否。必非朱子所编经传通解也。岂以曲礼少仪。合称仪礼否。曲少之外。抑果指他书也。
许氏小学大义
按。鲁斋以内篇。为小学之本源。外篇。为小学之支流。愚意篇名虽分内外。其实则只是一事。盖此纲领。只是立教明伦敬身三者而已。谓稽古者。即以汉以前圣贤所行之事。以实上篇三者之言而已。至于嘉言善行。又以汉以后贤者所言与所行。即广其义。而又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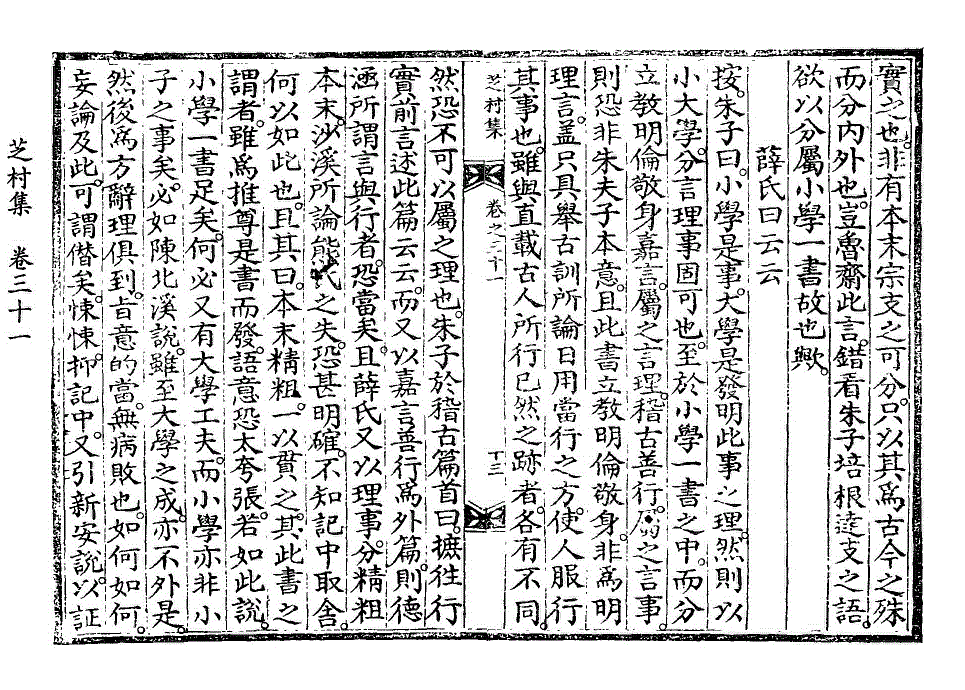 实之也。非有本末宗支之可分。只以其为古今之殊而分内外也。岂鲁斋此言。错看朱子培根达支之语。欲以分属小学一书故也欤。
实之也。非有本末宗支之可分。只以其为古今之殊而分内外也。岂鲁斋此言。错看朱子培根达支之语。欲以分属小学一书故也欤。薛氏曰云云
按。朱子曰。小学是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然则以小大学。分言理事固可也。至于小学一书之中。而分立教明伦敬身嘉言。属之言理。稽古善行。属之言事。则恐非朱夫子本意。且此书立教明伦敬身。非为明理言。盖只具举古训所论日用当行之方。使人服行其事也。虽与直载古人所行已然之迹者。各有不同。然恐不可以属之理也。朱子于稽古篇首曰。摭往行实前言述此篇云云。而又以嘉言善行为外篇。则德涵所谓言与行者。恐当矣。且薛氏又以理事。分精粗本末。沙溪所论熊氏之失。恐甚明确。不知记中取舍。何以如此也。且其曰。本末精粗。一以贯之。其此书之谓者。虽为推尊是书而发。语意恐太夸张。若如此说。小学一书足矣。何必又有大学工夫。而小学亦非小子之事矣。必如陈北溪说。虽至大学之成。亦不外是。然后为方辞理俱到。旨意的当。无病败也。如何如何。妄论及此。可谓僭矣。悚悚。抑记中。又引新安说。以证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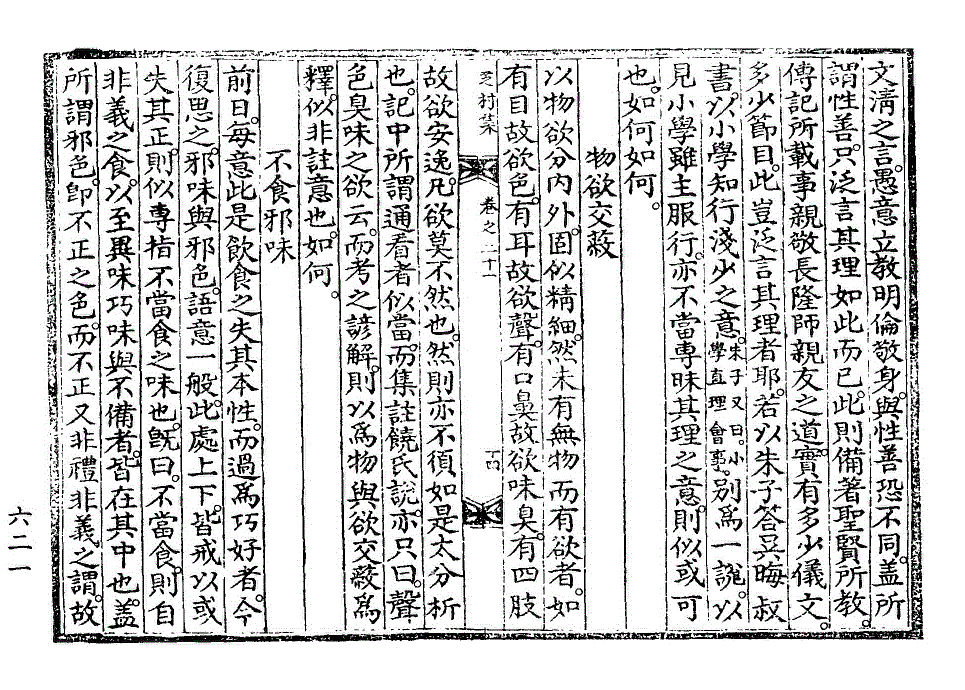 文清之言。愚意立教明伦敬身。与性善恐不同。盖所谓性善。只泛言其理如此而已。此则备著圣贤所教。传记所载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实有多少仪文。多少节目。此岂泛言其理者耶。若以朱子答吴晦叔书。以小学知行浅少之意。(朱子又曰。小学直理会事。)别为一说。以见小学虽主服行。亦不当专昧其理之意。则似或可也。如何如何。
文清之言。愚意立教明伦敬身。与性善恐不同。盖所谓性善。只泛言其理如此而已。此则备著圣贤所教。传记所载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实有多少仪文。多少节目。此岂泛言其理者耶。若以朱子答吴晦叔书。以小学知行浅少之意。(朱子又曰。小学直理会事。)别为一说。以见小学虽主服行。亦不当专昧其理之意。则似或可也。如何如何。物欲交蔽
以物欲分内外。固似精细。然未有无物而有欲者。如有目故欲色。有耳故欲声。有口鼻故欲味臭。有四肢故欲安逸。凡欲莫不然也。然则亦不须如是太分析也。记中所谓通看者似当。而集注饶氏说。亦只曰。声色臭味之欲云。而考之谚解。则以为物与欲交蔽为释。似非注意也。如何。
不食邪味
前日。每意此是饮食之失其本性。而过为巧好者。今复思之。邪味与邪色。语意一般。此处上下。皆戒以或失其正。则似专指不当食之味也。既曰。不当食。则自非义之食。以至异味巧味与不备者。皆在其中也。盖所谓邪色。即不正之色。而不正又非礼非义之谓。故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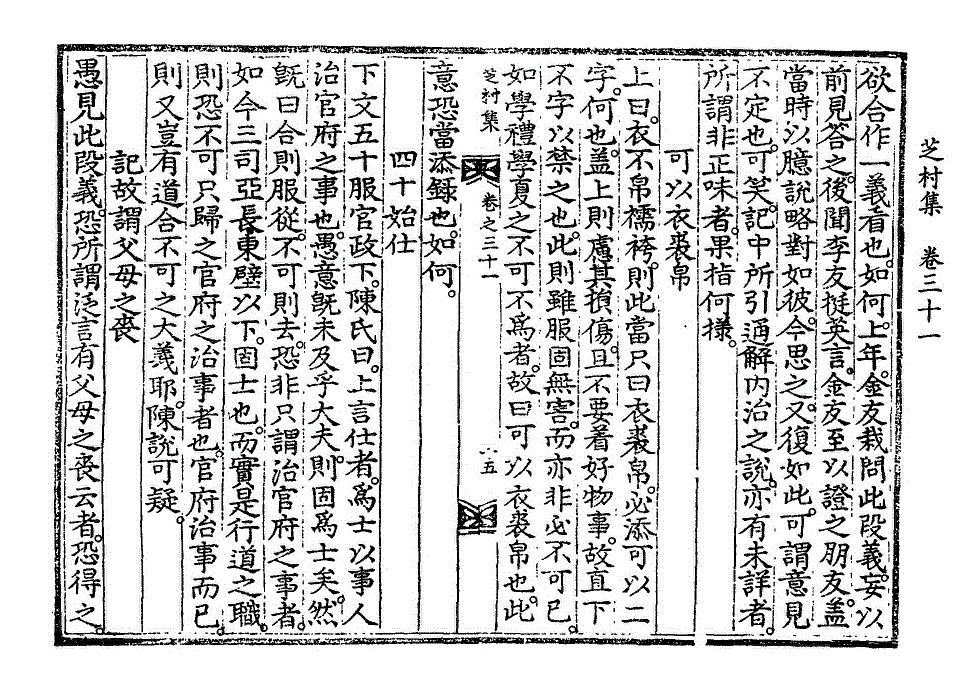 欲合作一义看也。如何。上年。金友栽问此段义。妄以前见答之。后闻李友挺英言。金友至以證之朋友。盖当时以臆说略对如彼。今思之。又复如此。可谓意见不定也。可笑。记中所引通解内治之说。亦有未详者。所谓非正味者。果指何㨾。
欲合作一义看也。如何。上年。金友栽问此段义。妄以前见答之。后闻李友挺英言。金友至以證之朋友。盖当时以臆说略对如彼。今思之。又复如此。可谓意见不定也。可笑。记中所引通解内治之说。亦有未详者。所谓非正味者。果指何㨾。可以衣裘帛
上曰。衣不帛襦裤。则此当只曰衣裘帛。必添可以二字。何也。盖上则虑其损伤。且不要着好物事。故直下不字以禁之也。此则虽服固无害。而亦非必不可已。如学礼学夏之不可不为者。故曰可以衣裘帛也。此意恐当添录也。如何。
四十始仕
下文五十服官政下。陈氏曰。上言仕者。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事也。愚意既未及乎大夫。则固为士矣。然既曰合则服从。不可则去。恐非只谓治官府之事者。如今三司亚长,东壁以下。固士也。而实是行道之职。则恐不可只归之官府之治事者也。官府治事而已。则又岂有道合不可之大义耶。陈说可疑。
记故谓父母之丧
愚见此段义。恐所谓泛言有父母之丧云者。恐得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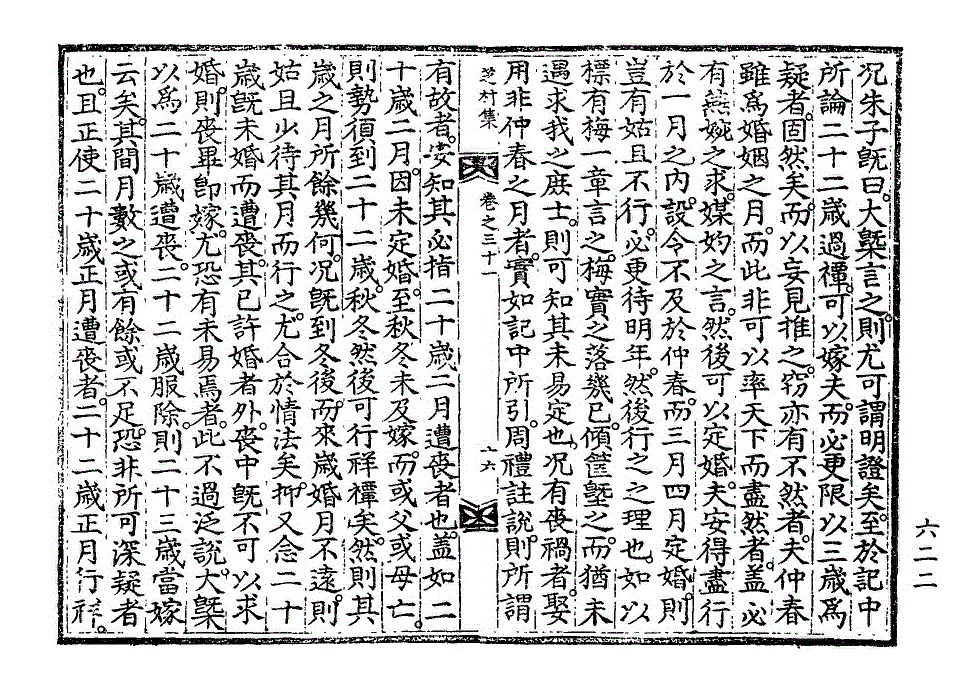 况朱子既曰。大槩言之。则尤可谓明證矣。至于记中所论二十二岁过禫。可以嫁夫。而必更限以三岁为疑者。固然矣。而以妄见推之。窃亦有不然者。夫仲春虽为婚姻之月。而此非可以率天下而尽然者。盖必有燕婉之求。媒妁之言。然后可以定婚。夫安得尽行于一月之内。设令不及于仲春。而三月四月定婚。则岂有姑且不行。必更待明年。然后行之之理也。如以标有梅一章言之。梅实之落几已。倾筐塈之。而犹未遇求我之庶士。则可知其未易定也。况有丧祸者。娶用非仲春之月者。实如记中所引。周礼注说。则所谓有故者。安知其必指二十岁二月遭丧者也。盖如二十岁二月。因未定婚。至秋冬未及嫁。而或父或母亡。则势须到二十二岁。秋冬然后可行祥禫矣。然则其岁之月所馀几何。况既到冬后。而来岁婚月不远。则姑且少待其月而行之。尤合于情法矣。抑又念二十岁既未婚而遭丧。其已许婚者外。丧中既不可以求婚。则丧毕即嫁。尤恐有未易焉者。此不过泛说。大槩以为二十岁遭丧。二十二岁服除。则二十三岁当嫁云矣。其间月数之或有馀或不足。恐非所可深疑者也。且正使二十岁正月遭丧者。二十二岁正月行祥。
况朱子既曰。大槩言之。则尤可谓明證矣。至于记中所论二十二岁过禫。可以嫁夫。而必更限以三岁为疑者。固然矣。而以妄见推之。窃亦有不然者。夫仲春虽为婚姻之月。而此非可以率天下而尽然者。盖必有燕婉之求。媒妁之言。然后可以定婚。夫安得尽行于一月之内。设令不及于仲春。而三月四月定婚。则岂有姑且不行。必更待明年。然后行之之理也。如以标有梅一章言之。梅实之落几已。倾筐塈之。而犹未遇求我之庶士。则可知其未易定也。况有丧祸者。娶用非仲春之月者。实如记中所引。周礼注说。则所谓有故者。安知其必指二十岁二月遭丧者也。盖如二十岁二月。因未定婚。至秋冬未及嫁。而或父或母亡。则势须到二十二岁。秋冬然后可行祥禫矣。然则其岁之月所馀几何。况既到冬后。而来岁婚月不远。则姑且少待其月而行之。尤合于情法矣。抑又念二十岁既未婚而遭丧。其已许婚者外。丧中既不可以求婚。则丧毕即嫁。尤恐有未易焉者。此不过泛说。大槩以为二十岁遭丧。二十二岁服除。则二十三岁当嫁云矣。其间月数之或有馀或不足。恐非所可深疑者也。且正使二十岁正月遭丧者。二十二岁正月行祥。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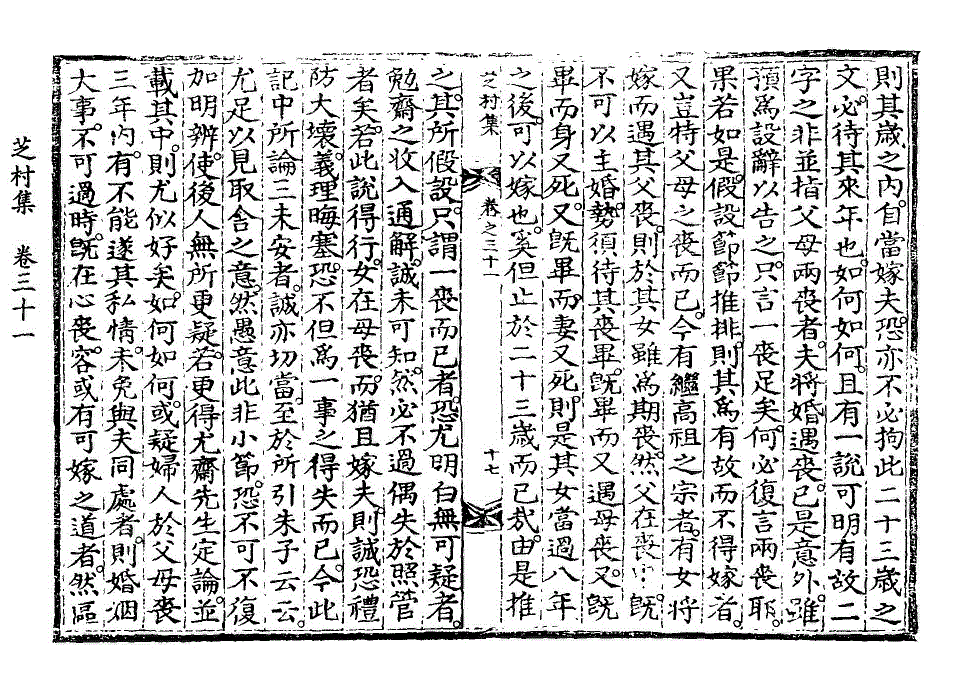 则其岁之内。自当嫁夫。恐亦不必拘此二十三岁之文。必待其来年也。如何如何。且有一说可明有故二字之非并指父母两丧者。夫将婚遇丧。已是意外。虽预为设辞以告之。只言一丧足矣。何必复言两丧耶。果若如是。假设节节推排。则其为有故而不得嫁者。又岂特父母之丧而已。今有继高祖之宗者。有女将嫁而遇其父丧。则于其女虽为期丧。然父在丧中。既不可以主婚。势须待其丧毕。既毕而又遇母丧。又既毕而身又死。又既毕。而妻又死。则是其女当过八年之后。可以嫁也。奚但止于二十三岁而已哉。由是推之。其所假设。只谓一丧而已者。恐尤明白无可疑者。勉斋之收入通解。诚未可知。然必不过偶失于照管者矣。若此说得行。女在母丧。而犹且嫁夫。则诚恐礼防大坏。义理晦塞。恐不但为一事之得失而已。今此记中所论三未安者。诚亦切当。至于所引朱子云云。尤足以见取舍之意。然愚意此非小节。恐不可不复加明辨。使后人无所更疑。若更得尤斋先生定论。并载其中。则尤似好矣。如何如何。或疑妇人于父母丧三年内。有不能遂其私情。未免与夫同处者。则婚姻大事。不可过时。既在心丧。容或有可嫁之道者。然区
则其岁之内。自当嫁夫。恐亦不必拘此二十三岁之文。必待其来年也。如何如何。且有一说可明有故二字之非并指父母两丧者。夫将婚遇丧。已是意外。虽预为设辞以告之。只言一丧足矣。何必复言两丧耶。果若如是。假设节节推排。则其为有故而不得嫁者。又岂特父母之丧而已。今有继高祖之宗者。有女将嫁而遇其父丧。则于其女虽为期丧。然父在丧中。既不可以主婚。势须待其丧毕。既毕而又遇母丧。又既毕而身又死。又既毕。而妻又死。则是其女当过八年之后。可以嫁也。奚但止于二十三岁而已哉。由是推之。其所假设。只谓一丧而已者。恐尤明白无可疑者。勉斋之收入通解。诚未可知。然必不过偶失于照管者矣。若此说得行。女在母丧。而犹且嫁夫。则诚恐礼防大坏。义理晦塞。恐不但为一事之得失而已。今此记中所论三未安者。诚亦切当。至于所引朱子云云。尤足以见取舍之意。然愚意此非小节。恐不可不复加明辨。使后人无所更疑。若更得尤斋先生定论。并载其中。则尤似好矣。如何如何。或疑妇人于父母丧三年内。有不能遂其私情。未免与夫同处者。则婚姻大事。不可过时。既在心丧。容或有可嫁之道者。然区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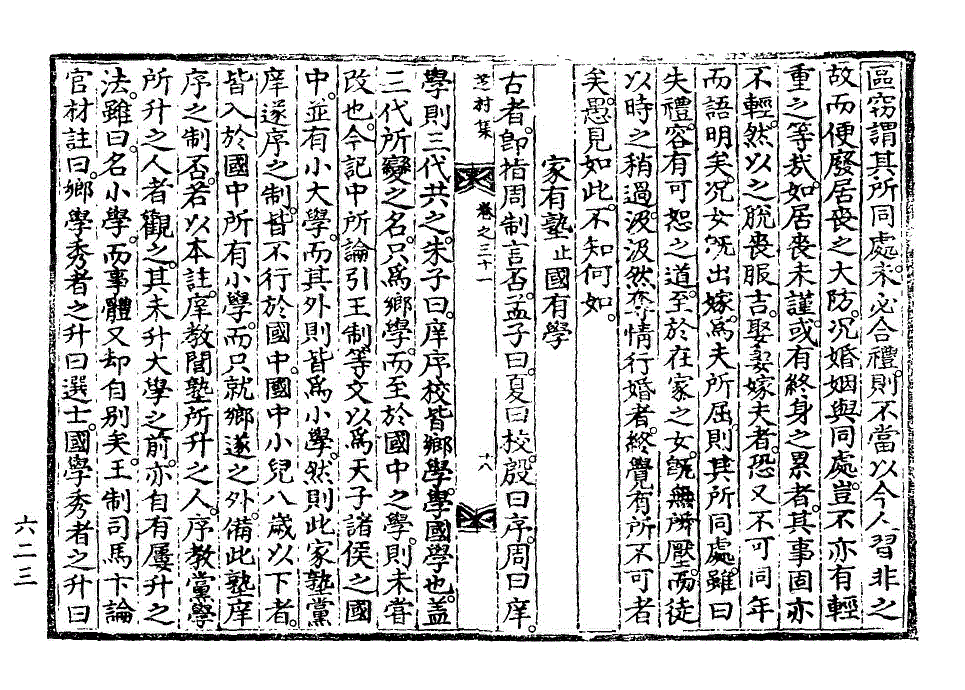 区窃谓其所同处。未必合礼。则不当以今人习非之故而便废居丧之大防。况婚姻与同处。岂不亦有轻重之等哉。如居丧未谨。或有终身之累者。其事固亦不轻。然以之脱丧服吉。娶妻嫁夫者。恐又不可同年而语明矣。况女既出嫁。为夫所屈。则其所同处。虽曰失礼。容有可恕之道。至于在家之女。既无所压。而徒以时之稍过。汲汲然夺情行婚者。终觉有所不可者矣。愚见如此。不知何如。
区窃谓其所同处。未必合礼。则不当以今人习非之故而便废居丧之大防。况婚姻与同处。岂不亦有轻重之等哉。如居丧未谨。或有终身之累者。其事固亦不轻。然以之脱丧服吉。娶妻嫁夫者。恐又不可同年而语明矣。况女既出嫁。为夫所屈。则其所同处。虽曰失礼。容有可恕之道。至于在家之女。既无所压。而徒以时之稍过。汲汲然夺情行婚者。终觉有所不可者矣。愚见如此。不知何如。家有塾止国有学
古者。即指周制言否。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朱子曰。庠序校皆乡学。学国学也。盖三代所变之名。只为乡学。而至于国中之学。则未尝改也。今记中所论引王制等文以为天子诸侯之国中。并有小大学。而其外则皆为小学。然则此家塾党庠遂序之制。皆不行于国中。国中小儿八岁以下者。皆入于国中所有小学。而只就乡遂之外。备此塾庠序之制否。若以本注。庠教闾塾所升之人。序教党学所升之人者观之。其未升大学之前。亦自有屡升之法。虽曰。名小学。而事体又却自别矣。王制司马卞论官材注曰。乡学秀者之升曰选士。国学秀者之升曰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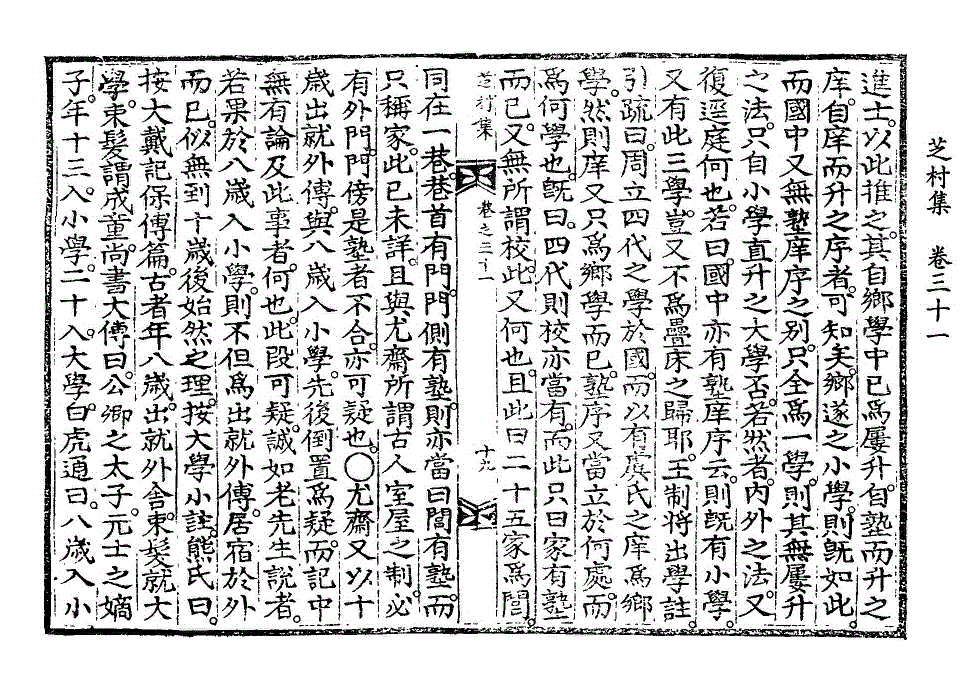 进士。以此推之。其自乡学中已为屡升。自塾而升之庠。自庠而升之序者。可知矣。乡遂之小学。则既如此。而国中又无塾庠序之别。只全为一学。则其无屡升之法。只自小学直升之大学否。若然者。内外之法。又复径庭何也。若曰。国中亦有塾庠序云。则既有小学。又有此三学。岂又不为叠床之归耶。王制将出学注。引疏曰。周立四代之学于国。而以有虞氏之庠为乡学。然则庠又只为乡学而已。塾序又当立于何处。而为何学也。既曰。四代则校亦当有。而此只曰家有塾而已。又无所谓校。此又何也。且此曰二十五家为闾。同在一巷。巷首有门。门侧有塾。则亦当曰闾有塾。而只称家。此已未详。且与尤斋所谓古人室屋之制。必有外门。门傍是塾者不合。亦可疑也。○尤斋又以十岁出就外傅。与八岁入小学。先后倒置为疑。而记中无有论及此事者。何也。此段可疑。诚如老先生说者。若果于八岁入小学。则不但为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而已。似无到十岁后始然之理。按大学小注。熊氏曰。按大戴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出就外舍。束发就大学。束发谓成童。尚书大传曰。公乡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白虎通曰。八岁入小
进士。以此推之。其自乡学中已为屡升。自塾而升之庠。自庠而升之序者。可知矣。乡遂之小学。则既如此。而国中又无塾庠序之别。只全为一学。则其无屡升之法。只自小学直升之大学否。若然者。内外之法。又复径庭何也。若曰。国中亦有塾庠序云。则既有小学。又有此三学。岂又不为叠床之归耶。王制将出学注。引疏曰。周立四代之学于国。而以有虞氏之庠为乡学。然则庠又只为乡学而已。塾序又当立于何处。而为何学也。既曰。四代则校亦当有。而此只曰家有塾而已。又无所谓校。此又何也。且此曰二十五家为闾。同在一巷。巷首有门。门侧有塾。则亦当曰闾有塾。而只称家。此已未详。且与尤斋所谓古人室屋之制。必有外门。门傍是塾者不合。亦可疑也。○尤斋又以十岁出就外傅。与八岁入小学。先后倒置为疑。而记中无有论及此事者。何也。此段可疑。诚如老先生说者。若果于八岁入小学。则不但为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而已。似无到十岁后始然之理。按大学小注。熊氏曰。按大戴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出就外舍。束发就大学。束发谓成童。尚书大传曰。公乡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白虎通曰。八岁入小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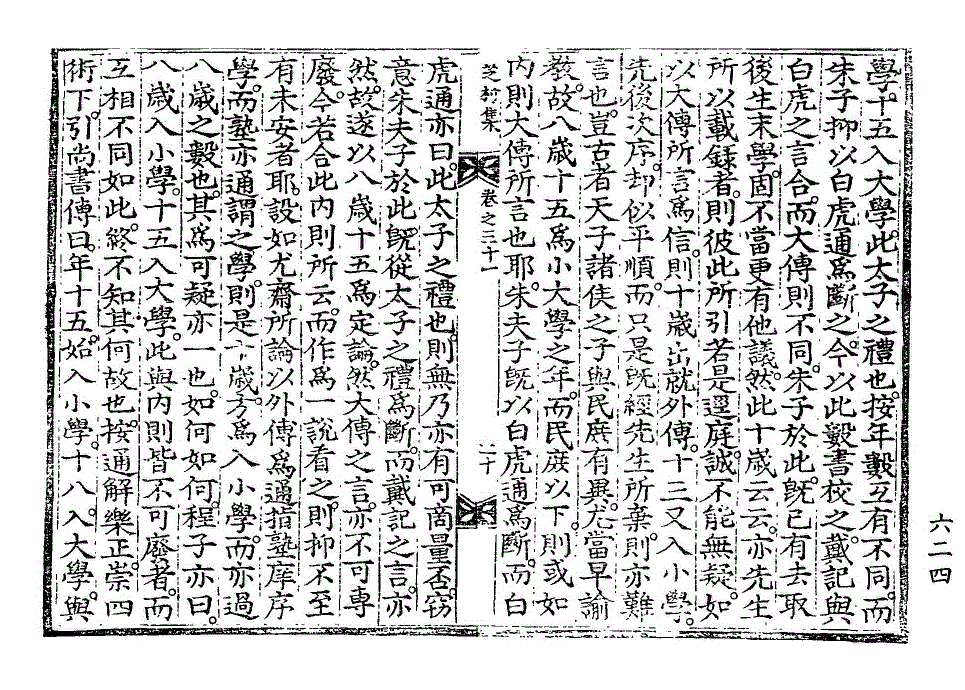 学。十五入大学。此太子之礼也。按年数互有不同。而朱子抑以白虎通为断之。今以此数书校之。戴记与白虎之言合。而大传则不同。朱子于此。既已有去取后生末学。固不当更有他议。然此十岁云云。亦先生所以载录者。则彼此所引若是径庭。诚不能无疑。如以大传所言为信。则十岁出就外傅。十三又入小学。先后次序。却似平顺。而只是既经先生所弃。则亦难言也。岂古者天子诸侯之子与民庶有异。尤当早谕教。故八岁十五为小大学之年。而民庶以下。则或如内则大传所言也耶。朱夫子既以白虎通为断。而白虎通亦曰。此太子之礼也。则无乃亦有可商量否。窃意朱夫子于此。既从太子之礼为断。而戴记之言。亦然。故遂以八岁十五为定论。然大传之言。亦不可专废。今若合此内则所云。而作为一说看之。则抑不至有未安者耶。设如尤斋所论以外傅为通指塾庠序学。而塾亦通谓之学。则是十岁。方为入小学。而亦过八岁之数也。其为可疑亦一也。如何如何。程子亦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与内则皆不可废者。而互相不同如此。终不知其何故也。按通解乐正。崇四术下。引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与
学。十五入大学。此太子之礼也。按年数互有不同。而朱子抑以白虎通为断之。今以此数书校之。戴记与白虎之言合。而大传则不同。朱子于此。既已有去取后生末学。固不当更有他议。然此十岁云云。亦先生所以载录者。则彼此所引若是径庭。诚不能无疑。如以大传所言为信。则十岁出就外傅。十三又入小学。先后次序。却似平顺。而只是既经先生所弃。则亦难言也。岂古者天子诸侯之子与民庶有异。尤当早谕教。故八岁十五为小大学之年。而民庶以下。则或如内则大传所言也耶。朱夫子既以白虎通为断。而白虎通亦曰。此太子之礼也。则无乃亦有可商量否。窃意朱夫子于此。既从太子之礼为断。而戴记之言。亦然。故遂以八岁十五为定论。然大传之言。亦不可专废。今若合此内则所云。而作为一说看之。则抑不至有未安者耶。设如尤斋所论以外傅为通指塾庠序学。而塾亦通谓之学。则是十岁。方为入小学。而亦过八岁之数也。其为可疑亦一也。如何如何。程子亦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与内则皆不可废者。而互相不同如此。终不知其何故也。按通解乐正。崇四术下。引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与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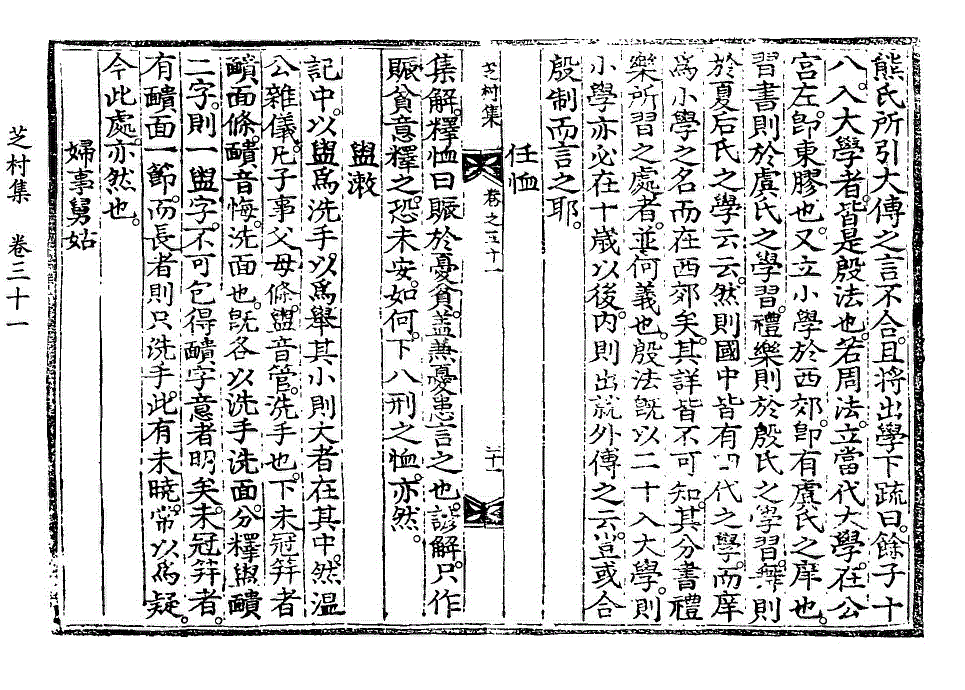 熊氏所引大传之言不合。且将出学下疏曰。馀子十八。入大学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当代大学。在公宫左。即东胶也。又立小学于西郊。即有虞氏之庠也。习书则于虞氏之学习。礼乐则于殷氏之学习。舞则于夏后氏之学云云。然则国中皆有四代之学。而庠为小学之名而在西郊矣。其详皆不可知。其分书礼乐所习之处者。并何义也。殷法既以二十入大学。则小学亦必在十岁以后。内则出就外傅之云。岂或合殷制而言之耶。
熊氏所引大传之言不合。且将出学下疏曰。馀子十八。入大学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当代大学。在公宫左。即东胶也。又立小学于西郊。即有虞氏之庠也。习书则于虞氏之学习。礼乐则于殷氏之学习。舞则于夏后氏之学云云。然则国中皆有四代之学。而庠为小学之名而在西郊矣。其详皆不可知。其分书礼乐所习之处者。并何义也。殷法既以二十入大学。则小学亦必在十岁以后。内则出就外傅之云。岂或合殷制而言之耶。任恤
集解。释恤曰赈于忧贫。盖兼忧患言之也。谚解。只作赈贫意释之。恐未安。如何。下八刑之恤。亦然。
盥漱
记中。以盥为洗手。以为举其小则大者在其中。然温公杂仪。凡子事父母条。盥音管。洗手也。下未冠笄者靧面条。靧音悔。洗面也。既各以洗手洗面。分释盥靧二字。则一盥字。不可包得靧字意者明矣。未冠笄者。有靧面一节。而长者则只洗手。此有未晓。常以为疑。今此处。亦然也。
妇事舅姑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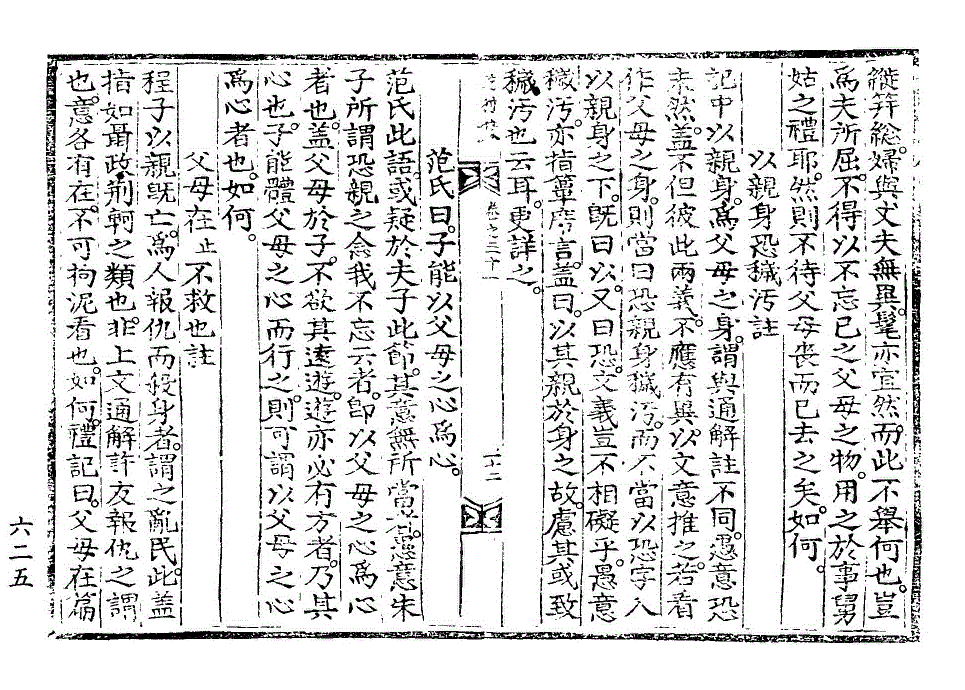 縰笄总。妇与丈夫无异。髦亦宜然。而此不举何也。岂为夫所屈。不得以不忘己之父母之物。用之于事舅姑之礼耶。然则不待父母丧而已去之矣。如何。
縰笄总。妇与丈夫无异。髦亦宜然。而此不举何也。岂为夫所屈。不得以不忘己之父母之物。用之于事舅姑之礼耶。然则不待父母丧而已去之矣。如何。以亲身恐秽污注
记中以亲身。为父母之身。谓与通解注不同。愚意恐未然。盖不但彼此两义。不应有异。以文意推之。若看作父母之身。则当曰恐亲身秽污。而不当以恐字入以亲身之下。既曰以。又曰恐。文义岂不相碍乎。愚意秽污。亦指簟席言。盖曰。以其亲于身之故。虑其或致秽污也云耳。更详之。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
范氏此语。或疑于夫子此节。其意无所当者。愚意朱子所谓恐亲之念我不忘云者。即以父母之心为心者也。盖父母于子。不欲其远游。游亦必有方者。乃其心也。子能体父母之心而行之。则可谓以父母之心为心者也。如何。
父母在止不救也注
程子以亲既亡。为人报仇而杀身者。谓之乱民。此盖指如聂政,荆轲之类也。非上文通解许友报仇之谓也。意各有在。不可拘泥看也。如何。礼记曰。父母在篇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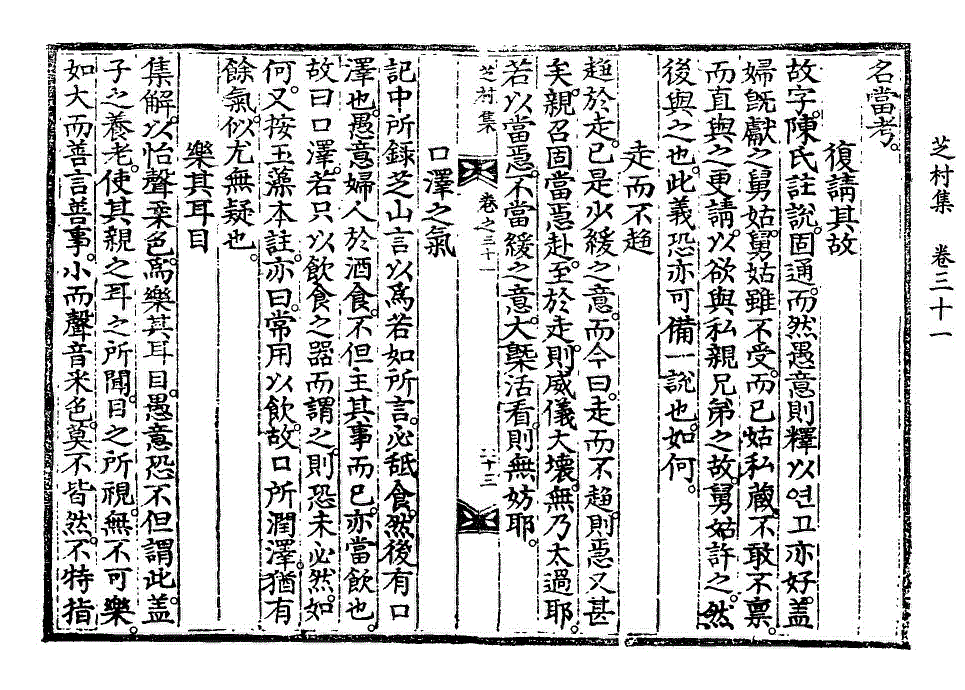 名当考。
名当考。复请其故
故字。陈氏注说。固通。而然愚意则释以연고亦好。盖妇既献之舅姑。舅姑虽不受。而已姑私藏。不敢不禀。而直与之更请。以欲与私亲兄弟之故。舅姑许之。然后与之也。此义恐亦可备一说也。如何。
走而不趋
趋于走。已是少缓之意。而今曰。走而不趋。则急又甚矣。亲召固当急赴。至于走。则威仪大坏。无乃太过耶。若以当急。不当缓之意。大槩活看。则无妨耶。
口泽之气
记中所录芝山言以为若如所言。必舐食。然后有口泽也。愚意妇人于酒食。不但主其事而已。亦当饮也。故曰口泽。若只以饮食之器而谓之。则恐未必然。如何。又按玉藻本注。亦曰。常用以饮。故口所润泽。犹有馀气。似尤无疑也。
乐其耳目
集解。以怡声柔色。为乐其耳目。愚意恐不但谓此。盖子之养老。使其亲之耳之所闻。目之所视。无不可乐。如大而善言善事。小而声音采色。莫不皆然。不特指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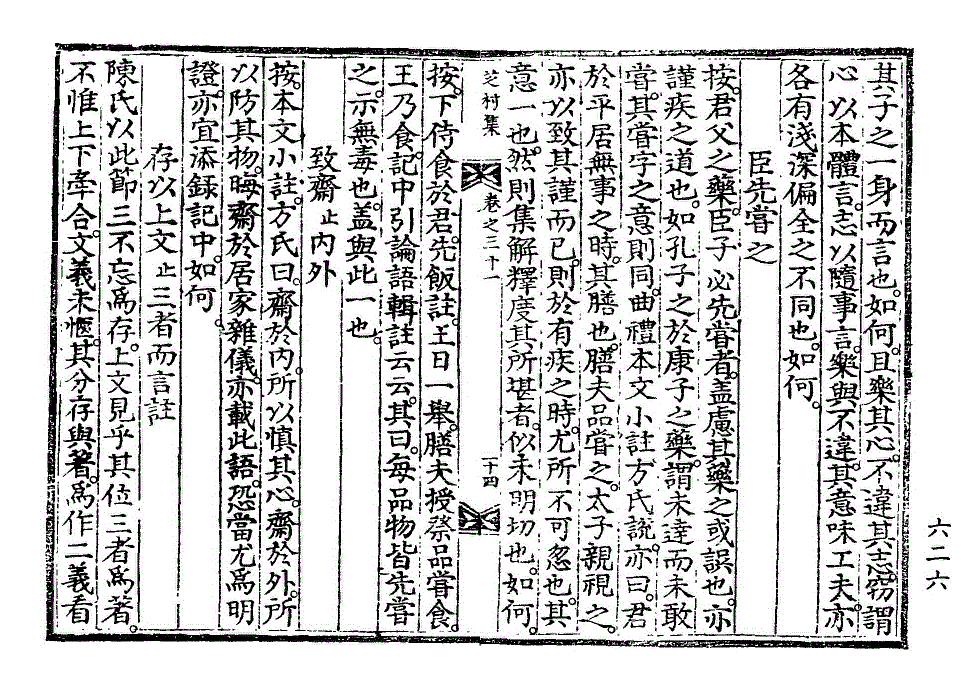 其子之一身而言也。如何。且乐其心。不违其志。窃谓心以本体言。志以随事言。乐与不违。其意味工夫。亦各有浅深偏全之不同也。如何。
其子之一身而言也。如何。且乐其心。不违其志。窃谓心以本体言。志以随事言。乐与不违。其意味工夫。亦各有浅深偏全之不同也。如何。臣先尝之
按。君父之药。臣子必先尝者。盖虑其药之或误也。亦谨疾之道也。如孔子之于康子之药。谓未达而未敢尝。其尝字之意则同。曲礼本文小注方氏说。亦曰。君于平居无事之时。其膳也。膳夫品尝之。太子亲视之。亦以致其谨而已。则于有疾之时。尤所不可忽也。其意一也。然则集解释度其所堪者。似未明切也。如何。按。下侍食于君。先饭注。王日一举。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记中引论语辑注云云。其曰。每品物皆先尝之。示无毒也。盖与此一也。
致斋止内外
按。本文小注。方氏曰。斋于内。所以慎其心。斋于外。所以防其物。晦斋于居家杂仪。亦载此语。恐当尤为明證。亦宜添录记中。如何。
存以上文止三者而言注
陈氏以此节三不忘为存。上文见乎其位三者为著。不惟上下牵合。文义未惬。其分存与著。为作二义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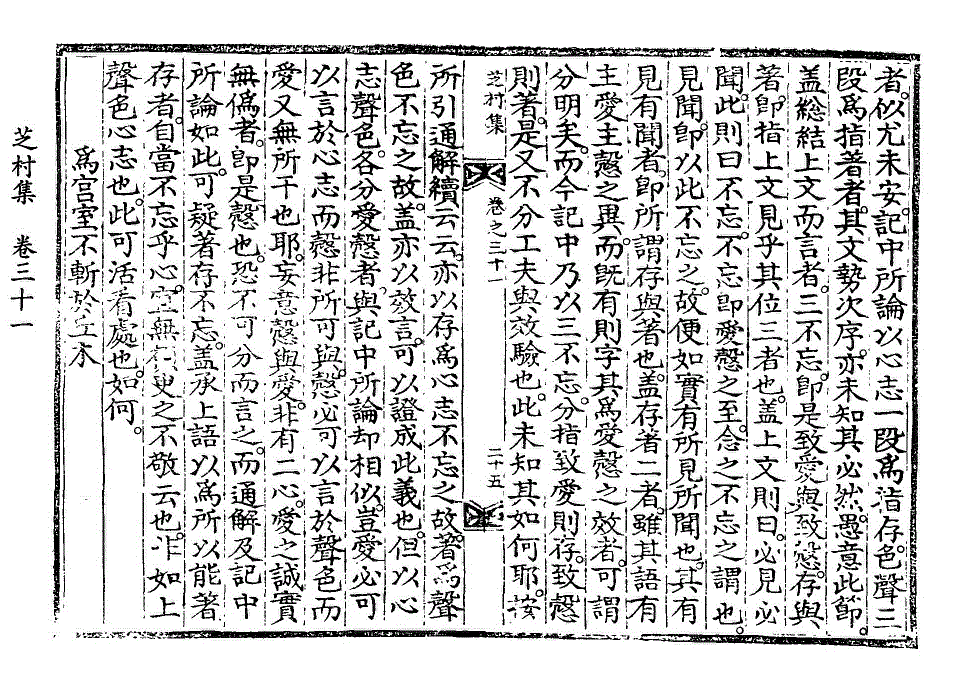 者。似尤未安。记中所论以心志一段为指存。色声三段为指著者。其文势次序。亦未知其必然。愚意此节。盖总结上文而言者。三不忘。即是致爱与致悫。存与著。即指上文见乎其位三者也。盖上文则曰。必见必闻。此则曰不忘。不忘即爱悫之至。念之不忘之谓也。见闻。即以此不忘之。故便如实有所见所闻也。其有见有闻者。即所谓存与著也。盖存著二者。虽其语有主爱主悫之异。而既有则字其为爱悫之效者。可谓分明矣。而今记中乃以三不忘。分指致爱则存。致悫则著。是又不分工夫与效验也。此未知其如何耶。按所引通解续云云。亦以存为心志不忘之故。著为声色不忘之故。盖亦以效言。可以證成此义也。但以心志声色。各分爱悫者。与记中所论却相似。岂爱必可以言于心志而悫非所可与。悫必可以言于声色而爱又无所干也耶。妄意悫与爱。非有二心。爱之诚实无伪者。即是悫也。恐不可分而言之。而通解及记中所论如此。可疑著存不忘。盖承上语以为所以能著存者。自当不忘乎心。宜无须臾之不敬云也。非如上声色心志也。此可活看处也。如何。
者。似尤未安。记中所论以心志一段为指存。色声三段为指著者。其文势次序。亦未知其必然。愚意此节。盖总结上文而言者。三不忘。即是致爱与致悫。存与著。即指上文见乎其位三者也。盖上文则曰。必见必闻。此则曰不忘。不忘即爱悫之至。念之不忘之谓也。见闻。即以此不忘之。故便如实有所见所闻也。其有见有闻者。即所谓存与著也。盖存著二者。虽其语有主爱主悫之异。而既有则字其为爱悫之效者。可谓分明矣。而今记中乃以三不忘。分指致爱则存。致悫则著。是又不分工夫与效验也。此未知其如何耶。按所引通解续云云。亦以存为心志不忘之故。著为声色不忘之故。盖亦以效言。可以證成此义也。但以心志声色。各分爱悫者。与记中所论却相似。岂爱必可以言于心志而悫非所可与。悫必可以言于声色而爱又无所干也耶。妄意悫与爱。非有二心。爱之诚实无伪者。即是悫也。恐不可分而言之。而通解及记中所论如此。可疑著存不忘。盖承上语以为所以能著存者。自当不忘乎心。宜无须臾之不敬云也。非如上声色心志也。此可活看处也。如何。为宫室不斩于丘木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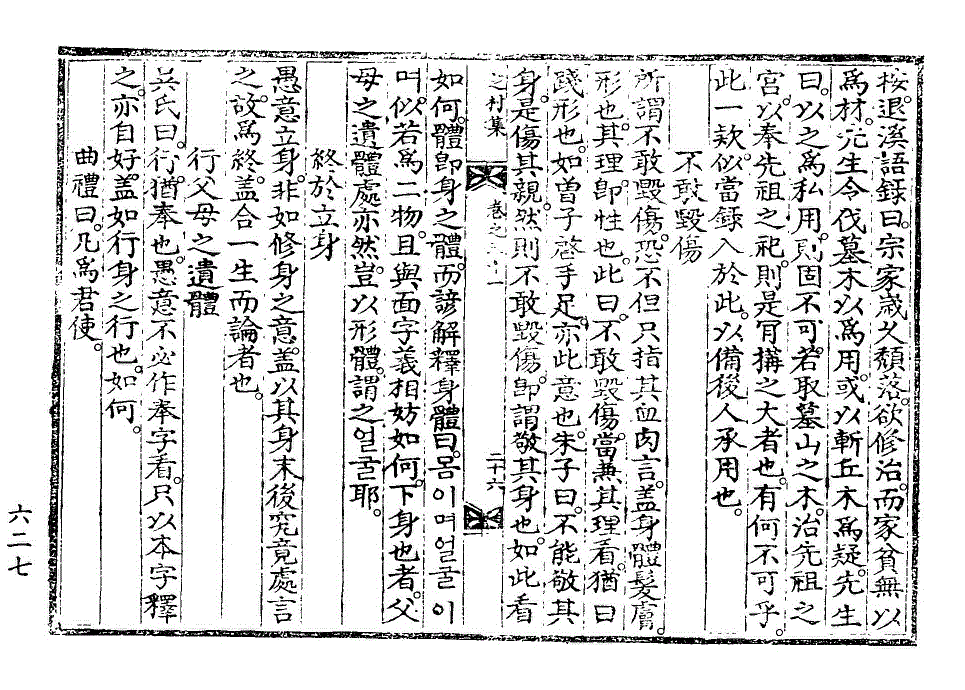 按。退溪语录曰。宗家岁久颓落。欲修治。而家贫无以为材。先生令伐墓木以为用。或以斩丘木为疑。先生曰。以之为私用。则固不可。若取墓山之木。治先祖之宫。以奉先祖之祀。则是肯搆之大者也。有何不可乎。此一款。似当录入于此。以备后人承用也。
按。退溪语录曰。宗家岁久颓落。欲修治。而家贫无以为材。先生令伐墓木以为用。或以斩丘木为疑。先生曰。以之为私用。则固不可。若取墓山之木。治先祖之宫。以奉先祖之祀。则是肯搆之大者也。有何不可乎。此一款。似当录入于此。以备后人承用也。不敢毁伤
所谓不敢毁伤。恐不但只指其血肉言。盖身体发肤。形也。其理。即性也。此曰。不敢毁伤。当兼其理看。犹曰践形也。如曾子启手足。亦此意也。朱子曰。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然则不敢毁伤。即谓敬其身也。如此看如何。体即身之体。而谚解释身体曰。몸이며얼굴이며。似若为二物。且与面字义相妨如何。下身也者。父母之遗体处亦然。岂以形体。谓之얼굴耶。
终于立身
愚意立身。非如修身之意。盖以其身末后究竟处言之。故为终。盖合一生而论者也。
行父母之遗体
吴氏曰。行。犹奉也。愚意不必作奉字看。只以本字释之。亦自好。盖如行身之行也。如何。
曲礼曰。凡为君使。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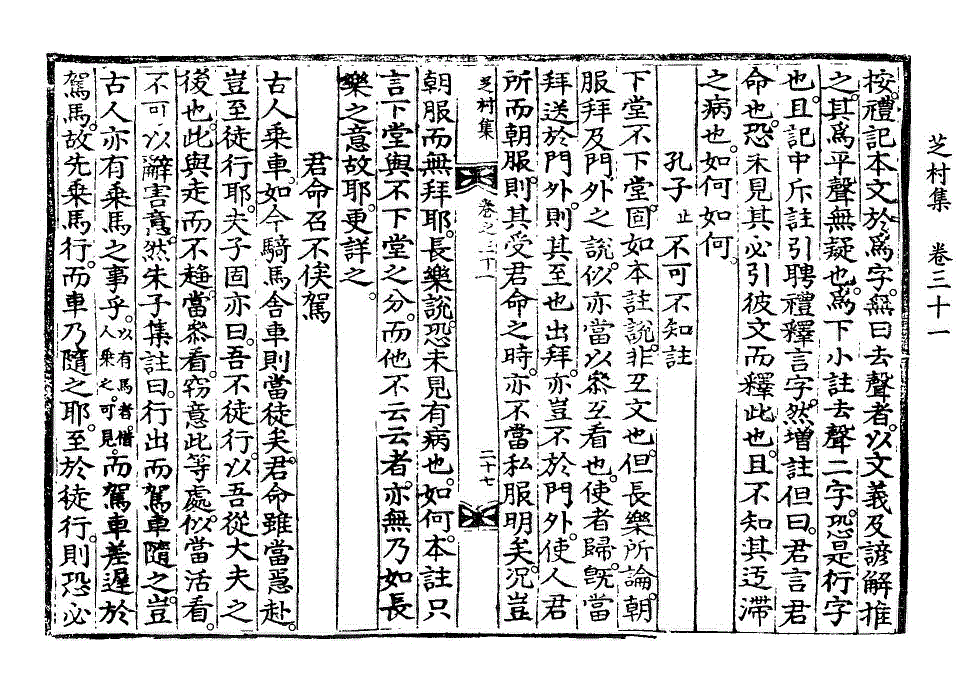 按。礼记本文于为字。无曰去声者。以文义及谚解推之。其为平声无疑也。为下小注去声二字。恐是衍字也。且记中斥注引聘礼释言字。然增注但曰。君言君命也。恐未见其必引彼文而释此也。且不知其迂滞之病也。如何如何。
按。礼记本文于为字。无曰去声者。以文义及谚解推之。其为平声无疑也。为下小注去声二字。恐是衍字也。且记中斥注引聘礼释言字。然增注但曰。君言君命也。恐未见其必引彼文而释此也。且不知其迂滞之病也。如何如何。孔子止不可不知注
下堂不下堂。固如本注说。非互文也。但长乐所论。朝服拜及门外之说。似亦当以参互看也。使者归。既当拜送于门外。则其至也出拜。亦岂不于门外。使人君所而朝服。则其受君命之时。亦不当私服明矣。况岂朝服而无拜耶。长乐说。恐未见有病也。如何。本注只言下堂与不下堂之分。而他不云云者。亦无乃如长乐之意故耶。更详之。
君命召不俟驾
古人乘车。如今骑马舍车则当徒矣。君命虽当急赴。岂至徒行耶。夫子固亦曰。吾不徒行。以吾从大夫之后也。此与走而不趋。当参看。窃意此等处。似当活看。不可以辞害意。然朱子集注曰。行出而驾车随之。岂古人亦有乘马之事乎。(以有马者。借人乘之。可见。)而驾车差迟于驾马。故先乘马行。而车乃随之耶。至于徒行。则恐必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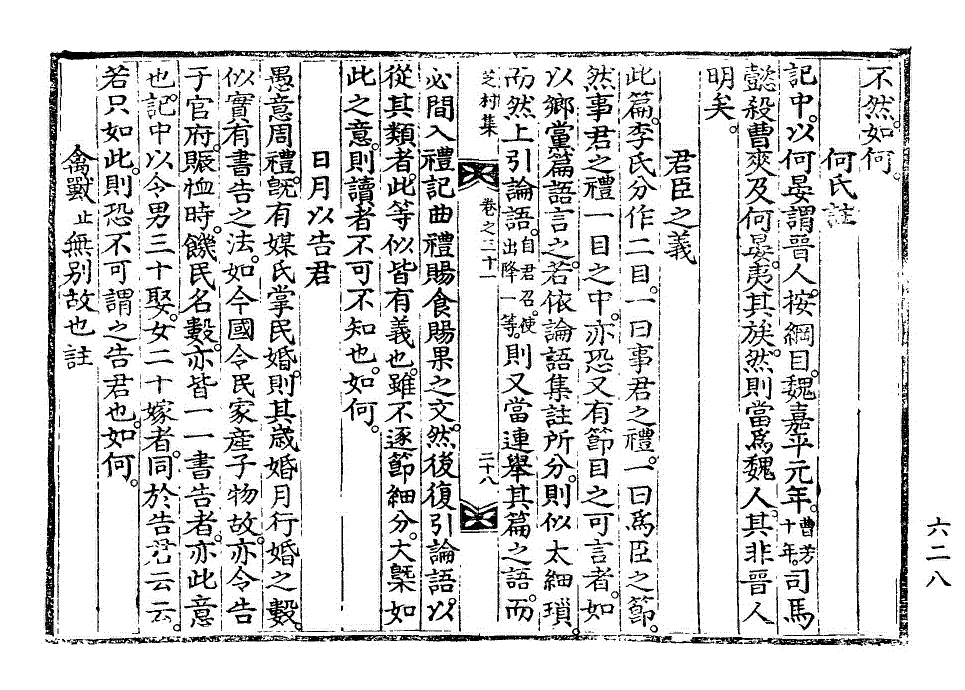 不然。如何。
不然。如何。何氏注
记中。以何晏谓晋人。按纲目。魏嘉平元年。(曹芳十年。)司马懿杀曹爽及何晏。夷其族。然则当为魏人。其非晋人明矣。
君臣之义
此篇。李氏分作二目。一曰事君之礼。一曰为臣之节。然事君之礼一目之中。亦恐又有节目之可言者。如以乡党篇语言之。若依论语集注所分。则似太细琐。而然上引论语。(自君召。使出降一等。)则又当连举其篇之语。而必间入礼记曲礼赐食赐果之文。然后复引论语。以从其类者。此等似皆有义也。虽不逐节细分。大槩如此之意。则读者不可不知也。如何。
日月以告君
愚意周礼。既有媒氏掌民婚。则其岁婚月行婚之数。似实有书告之法。如今国令民家产子物故。亦令告于官府。赈恤时。饥民名数。亦皆一一书告者。亦此意也。记中以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者。同于告君云云。若只如此。则恐不可谓之告君也。如何。
禽兽止无别故也注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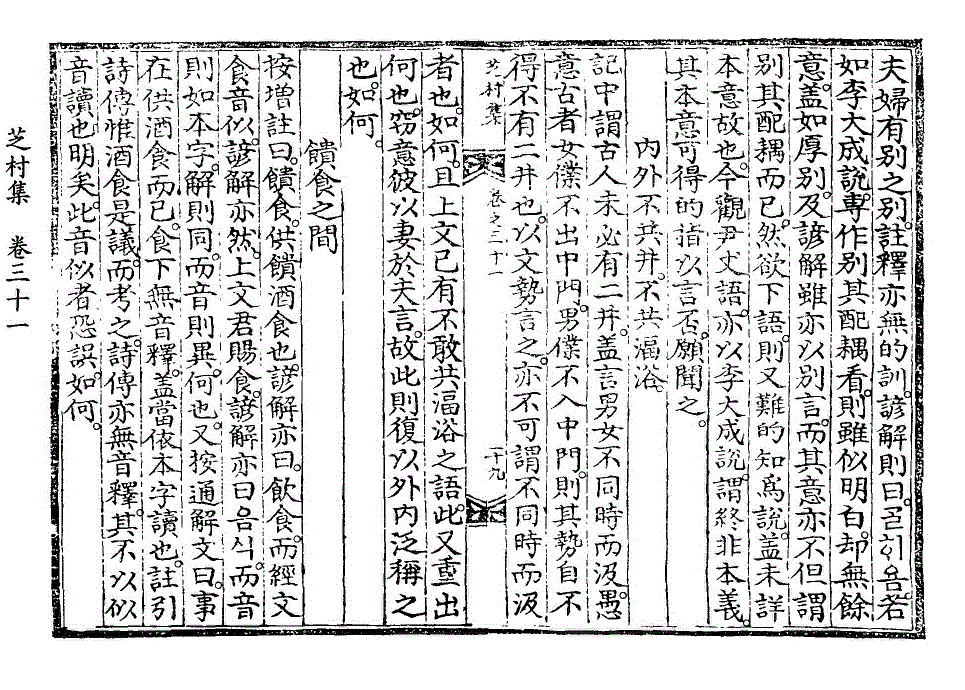 夫妇有别之别。注释亦无的训。谚解则曰。狸욤。若如李大成说。专作别其配耦看。则虽似明白。却无馀意。盖如厚别。及谚解虽亦以别言。而其意亦不但谓别其配耦而已。然欲下语。则又难的知为说。盖未详本意故也。今观尹丈语。亦以李大成说。谓终非本义。其本意可得的指以言否。愿闻之。
夫妇有别之别。注释亦无的训。谚解则曰。狸욤。若如李大成说。专作别其配耦看。则虽似明白。却无馀意。盖如厚别。及谚解虽亦以别言。而其意亦不但谓别其配耦而已。然欲下语。则又难的知为说。盖未详本意故也。今观尹丈语。亦以李大成说。谓终非本义。其本意可得的指以言否。愿闻之。内外不共井。不共湢浴。
记中谓古人未必有二井。盖言男女不同时而汲。愚意古者女仆不出中门。男仆不入中门。则其势自不得不有二井也。以文势言之。亦不可谓不同时而汲者也。如何。且上文已有不敢共湢浴之语。此又重出何也。窃意彼以妻于夫言。故此则复以外内泛称之也。如何。
馈食之间
按增注曰。馈食。供馈酒食也。谚解亦曰。饮食。而经文食音似。谚解亦然。上文君赐食。谚解亦曰음식。而音则如本字。解则同。而音则异。何也。又按通解文曰。事在供酒食而已。食下无音释。盖当依本字读也。注引诗传惟酒食是议。而考之。诗传亦无音释。其不以似音读也明矣。此音似者恐误。如何。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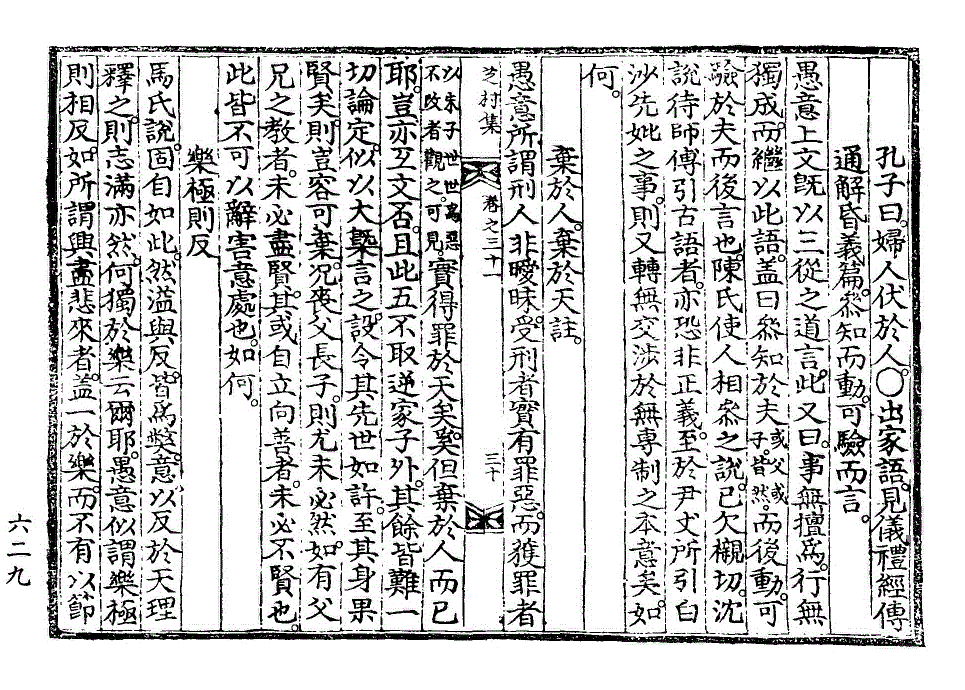 孔子曰。妇人伏于人。(出家语。见仪礼经传通解昏义篇。参知而动。可验而言。)
孔子曰。妇人伏于人。(出家语。见仪礼经传通解昏义篇。参知而动。可验而言。)愚意上文既以三从之道言。此又曰。事无擅为。行无独成。而继以此语。盖曰参知于夫(或父或子。皆然。)而后动。可验于夫而后言也。陈氏使人相参之说。已欠衬切。沈说待师傅引古语者。亦恐非正义。至于尹丈所引白沙先妣之事。则又转无交涉于无专制之本意矣。如何。
弃于人。弃于天注。
愚意所谓刑人非暧昧。受刑者实有罪恶。而获罪者(以朱子世世为恶不改者观之。可见。)实得罪于天矣。奚但弃于人而已耶。岂亦互文否。且此五不取逆家子外。其馀皆难一切论定。似以大槩言之。设令其先世如许。至其身果贤矣。则岂容可弃。况丧父长子。则尤未必然。如有父兄之教者。未必尽贤。其或自立向善者。未必不贤也。此皆不可以辞害意处也。如何。
乐极则反
马氏说。固自如此。然溢与反。皆为弊。意以反于天理释之。则志满亦然。何独于乐云尔耶。愚意似谓乐极则相反。如所谓兴尽悲来者。盖一于乐。而不有以节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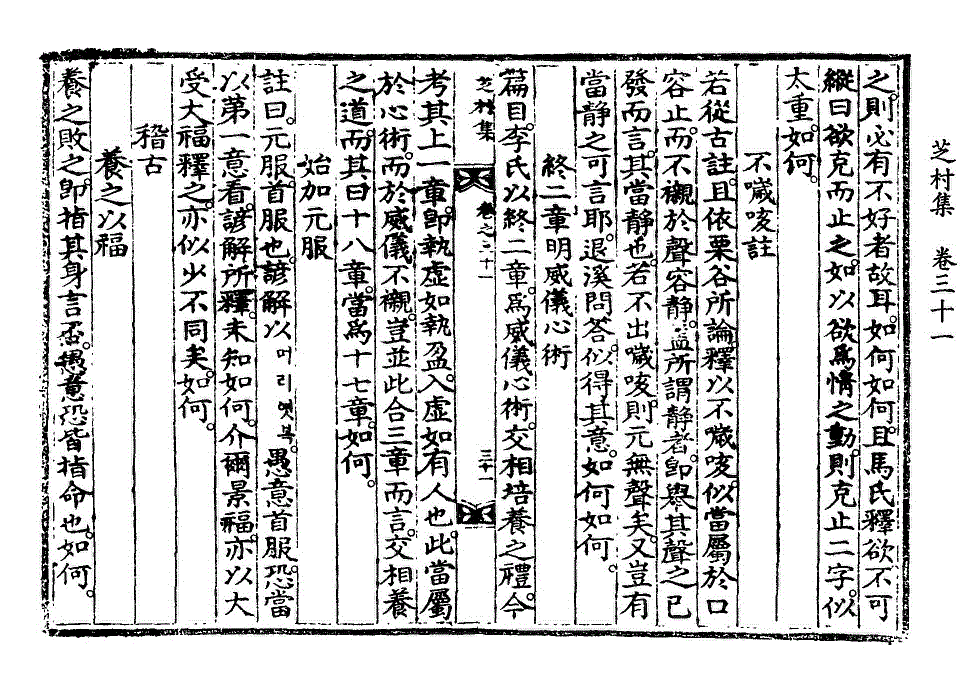 之。则必有不好者故耳。如何如何。且马氏释欲不可纵曰欲克而止之。如以欲为情之动。则克止二字。似太重。如何。
之。则必有不好者故耳。如何如何。且马氏释欲不可纵曰欲克而止之。如以欲为情之动。则克止二字。似太重。如何。不哕咳注
若从古注。且依栗谷所论。释以不哕咳。似当属于口容止。而不衬于声容静。盖所谓静者。即举其声之已发而言。其当静也。若不出哕咳。则元无声矣。又岂有当静之可言耶。退溪问答。似得其意。如何如何。
终二章明威仪心术
篇目。李氏以终二章。为威仪心术。交相培养之礼。今考其上一章。即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也。此当属于心术。而于威仪不衬。岂并此合三章而言。交相养之道。而其曰十八章。当为十七章。如何。
始加元服
注曰。元服。首服也。谚解以(머리엿복。)愚意首服。恐当以第一意看。谚解所释。未知如何。介尔景福。亦以大受大福释之。亦似少不同矣。如何。
稽古○养之以福
养之败之。即指其身言否。愚意恐皆指命也。如何。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0L 页
 诗传劄疑
诗传劄疑记序
按。序有小大。大即子夏所作。小即汉卫宏作。而朱子以为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者也。集传周南篇题。既引小序而曰。小序则后凡言序及旧说。皆当为指此小序言。盖上既曰小序。故后虽不更称小序。亦可见其为小序也。
小注朱子曰。此诗看来。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侧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此诗。以朱子所谓宫中之人于其始至。作是诗者。观之。可见其为宫人之诗矣。其曰。寤寐反侧。琴瑟钟鼓。皆宫人之事也。哀不伤乐不淫。亦谓宫人情性之正也。第八板辑注胡氏说。尤分明。惟是朱夫子此言可疑。若曰。宫人自道其己事。则有何形容云云。又安有外人做不到之说哉。岂夫子之意以为妾媵。自能形容其心。非外人所可及耶。且妾媵是从嫡而来者。后妃未来之前。亦有所谓妾媵否。岂泛指宫妾言否。且后人多以琴瑟。言于夫妻。或疑其本出于此。然此则乃出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语。非本于此也。如何。
第九板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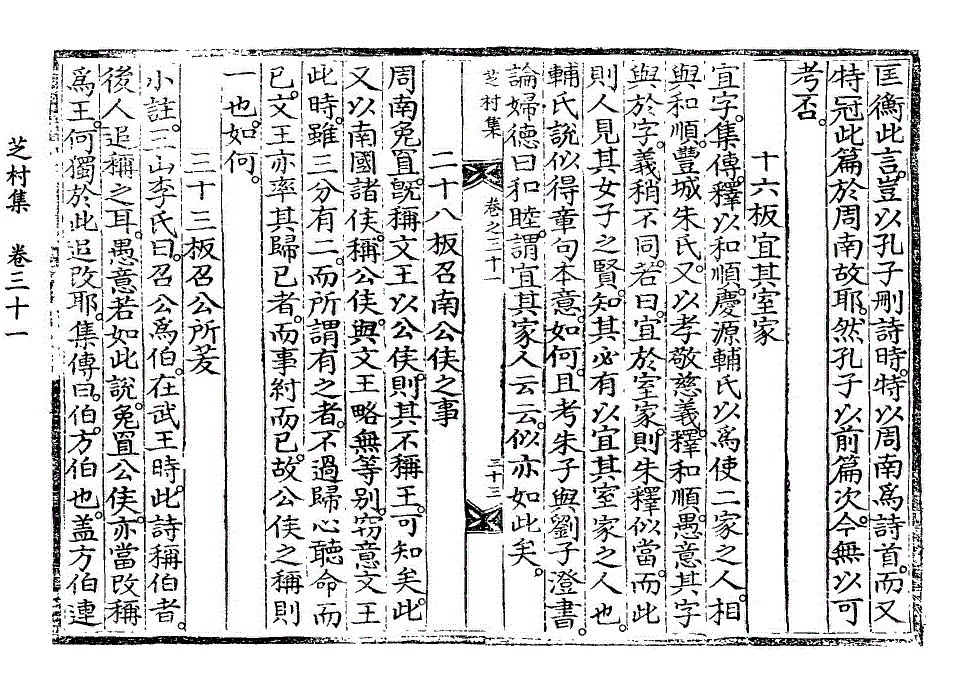 匡衡此言。岂以孔子删诗时。特以周南为诗首。而又特冠此篇于周南故耶。然孔子以前篇次。今无以可考否。
匡衡此言。岂以孔子删诗时。特以周南为诗首。而又特冠此篇于周南故耶。然孔子以前篇次。今无以可考否。十六板宜其室家
宜字。集传。释以和顺。庆源辅氏以为使二家之人。相与和顺。丰城朱氏。又以孝敬慈义。释和顺。愚意其字与于字。义稍不同。若曰。宜于室家。则朱释似当。而此则人见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之人也。辅氏说似得章句本意。如何。且考朱子与刘子澄书。论妇德曰和睦。谓宜其家人云云。似亦如此矣。
二十八板召南公侯之事
周南兔罝。既称文王以公侯。则其不称王。可知矣。此又以南国诸侯。称公侯。与文王略无等别。窃意文王此时。虽三分有二。而所谓有之者。不过归心听命而已。文王亦率其归己者。而事纣而已。故公侯之称则一也。如何。
三十三板召公所茇
小注。三山李氏曰。召公为伯。在武王时。此诗称伯者。后人追称之耳。愚意若如此说。兔罝公侯。亦当改称为王。何独于此追改耶。集传曰。伯。方伯也。盖方伯连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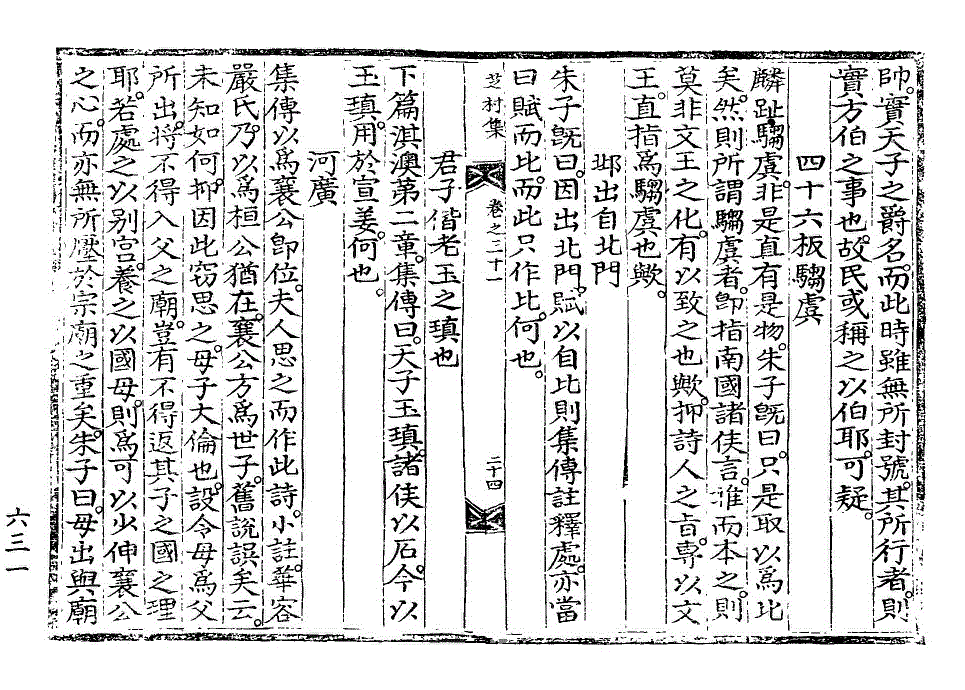 帅。实天子之爵名。而此时虽无所封号。其所行者。则实方伯之事也。故民或称之以伯耶。可疑。
帅。实天子之爵名。而此时虽无所封号。其所行者。则实方伯之事也。故民或称之以伯耶。可疑。四十六板驺虞
麟趾,驺虞。非是直有是物。朱子既曰。只是取以为比矣。然则所谓驺虞者。即指南国诸侯言。推而本之。则莫非文王之化。有以致之也欤。抑诗人之旨。专以文王。直指为驺虞也欤。
邶出自北门
朱子既曰。因出北门。赋以自比则集传注释处。亦当曰赋而比。而此只作比。何也。
君子偕老玉之瑱也
下篇淇澳第二章。集传曰。天子玉瑱。诸侯以石。今以玉瑱。用于宣姜。何也。
河广
集传以为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作此诗。小注。华容严氏。乃以为桓公犹在。襄公方为世子。旧说误矣云。未知如何。抑因此窃思之。母子大伦也。设令母为父所出。将不得入父之庙。岂有不得返其子之国之理耶。若处之以别宫。养之以国母。则为可以少伸襄公之心。而亦无所压于宗庙之重矣。朱子曰。母出与庙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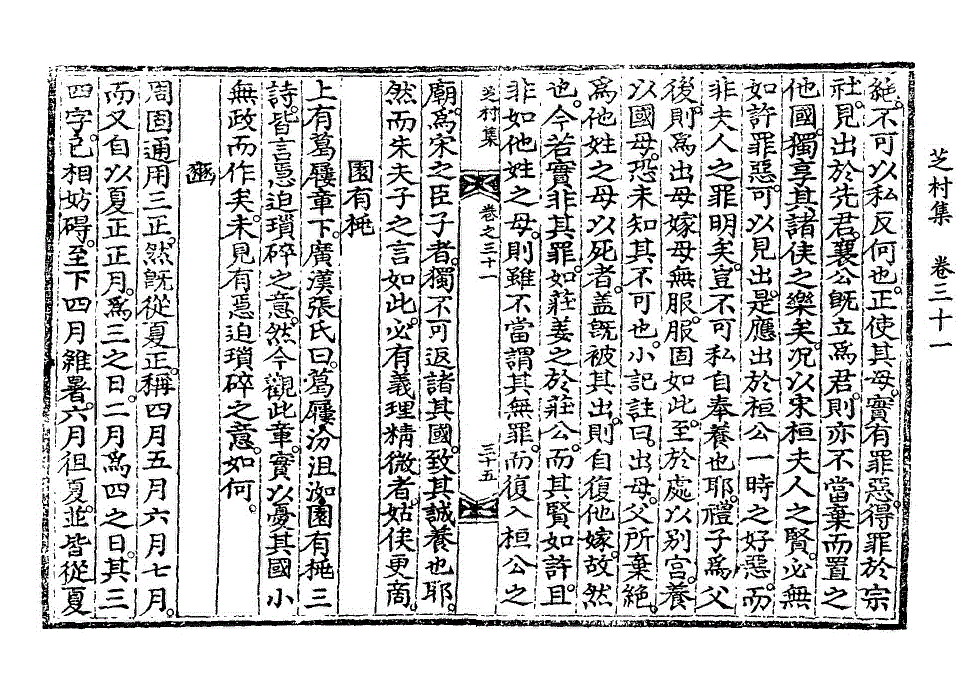 绝。不可以私反何也。正使其母。实有罪恶。得罪于宗社。见出于先君。襄公既立为君。则亦不当弃而置之他国。独享其诸侯之乐矣。况以宋桓夫人之贤。必无如许罪恶。可以见出。是应出于桓公一时之好恶。而非夫人之罪明矣。岂不可私自奉养也耶。礼子为父后。则为出母嫁母无服。服固如此。至于处以别宫。养以国母。恐未知其不可也。小记注曰。出母。父所弃绝。为他姓之母以死者。盖既被其出。则自复他嫁。故然也。今若实非其罪。如庄姜之于庄公。而其贤如许。且非如他姓之母。则虽不当谓其无罪。而复入桓公之庙。为宋之臣子者。独不可返诸其国。致其诚养也耶。然而朱夫子之言如此。必有义理精微者。姑俟更商。
绝。不可以私反何也。正使其母。实有罪恶。得罪于宗社。见出于先君。襄公既立为君。则亦不当弃而置之他国。独享其诸侯之乐矣。况以宋桓夫人之贤。必无如许罪恶。可以见出。是应出于桓公一时之好恶。而非夫人之罪明矣。岂不可私自奉养也耶。礼子为父后。则为出母嫁母无服。服固如此。至于处以别宫。养以国母。恐未知其不可也。小记注曰。出母。父所弃绝。为他姓之母以死者。盖既被其出。则自复他嫁。故然也。今若实非其罪。如庄姜之于庄公。而其贤如许。且非如他姓之母。则虽不当谓其无罪。而复入桓公之庙。为宋之臣子者。独不可返诸其国。致其诚养也耶。然而朱夫子之言如此。必有义理精微者。姑俟更商。园有桃
上有葛屦章下。广汉张氏曰。葛屦,汾沮洳,园有桃三诗。皆言急迫琐碎之意。然今观此章。实以忧其国小无政而作矣。未见有急迫琐碎之意。如何。
豳
周固通用三正。然既从夏正。称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而又自以夏正正月。为三之日。二月为四之日。其三四字。已相妨碍。至下四月维暑。六月徂夏。并皆从夏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2L 页
 正言之。正月繁霜。则又以纯阳之月言。然则夏正正月之名。果如何否。
正言之。正月繁霜。则又以纯阳之月言。然则夏正正月之名。果如何否。韩奕
第四章。集传曰。诸侯一娶九女。二国媵之。皆有娣侄。小注。罗氏曰。侄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安城刘氏曰。嫡妻。有娣有侄。同姓。二国之媵。亦有娣有侄。则九女也。然则嫡妻既自有侄娣。二国媵。又各有娣侄。合为九女耶。
颂
颂。即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而周颂中。如臣工载芟等篇。非与于祭告之事。亦得为颂。何也。岂所谓当为豳颂者。诚然乎哉。周颂虽有屡章。而每合称曰一章。(如良耟之类。)鲁颂,商颂。又却不然。何也。且周颂则但于其章下称赋也。以见其下。皆为赋。而鲁,商二颂。亦依风雅之例。皆各著兴比赋。此又未详。以商颂言之。长发,殷武以一节为一章那。烈祖,玄鸟以一篇为一章。长发殷武。每节之下。皆曰赋。而其上三章。则只于初节下称之。并可疑。
駉
一章。集传曰。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小注。庆源辅氏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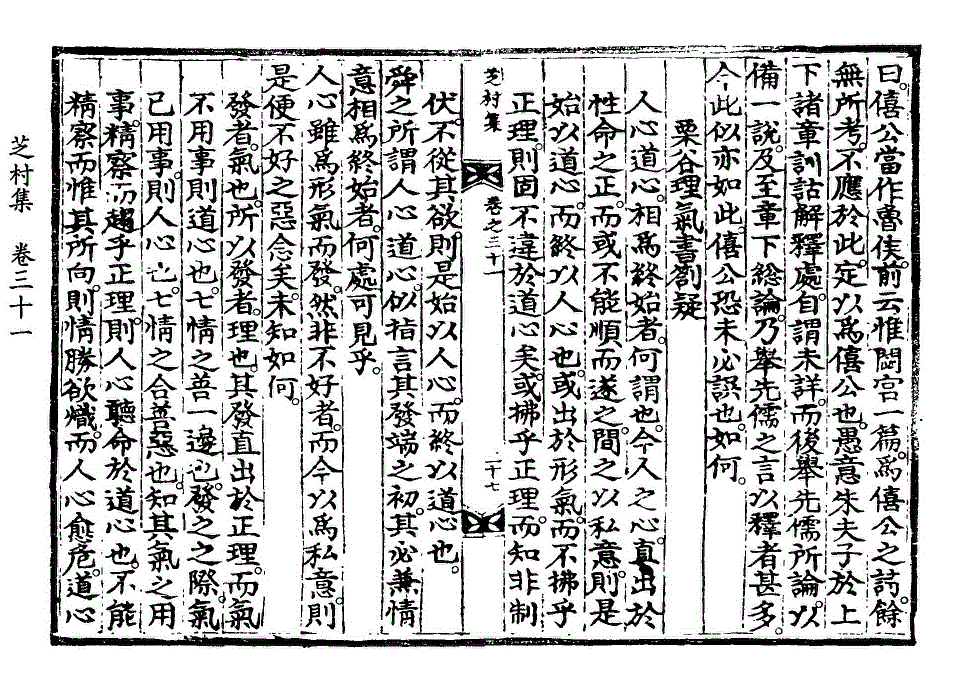 曰。僖公当作鲁侯。前云惟閟宫一篇。为僖公之诗。馀无所考。不应于此。定以为僖公也。愚意朱夫子于上下诸章训诂解释处。自谓未详。而后举先儒所论。以备一说。及至章下总论。乃举先儒之言以释者甚多。今此似亦如此。僖公恐未必误也。如何。
曰。僖公当作鲁侯。前云惟閟宫一篇。为僖公之诗。馀无所考。不应于此。定以为僖公也。愚意朱夫子于上下诸章训诂解释处。自谓未详。而后举先儒所论。以备一说。及至章下总论。乃举先儒之言以释者甚多。今此似亦如此。僖公恐未必误也。如何。栗谷理气书劄疑
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拂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拂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
舜之所谓人心道心。似指言其发端之初。其必兼情意相为终始者。何处可见乎。
人心虽为形气而发。然非不好者。而今以为私意。则是便不好之恶念矣。未知如何。
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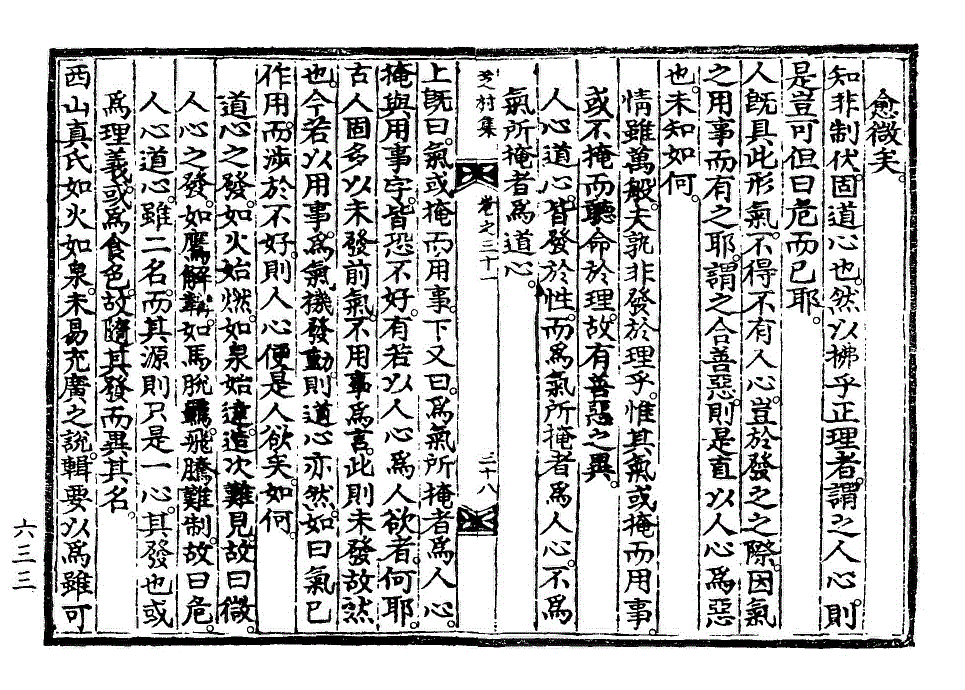 愈微矣。
愈微矣。知非制伏。固道心也。然以拂乎正理者。谓之人心。则是岂可但曰危而已耶。
人既具此形气。不得不有人心。岂于发之之际。因气之用事而有之耶。谓之合善恶。则是直以人心为恶也。未知如何。
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
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
上既曰。气或掩而用事。下又曰。为气所掩者为人心。掩与用事字。皆恐不好。有若以人心为人欲者。何耶。古人固多以未发前气。不用事为言。此则未发故然也。今若以用事。为气机发动。则道心亦然。如曰气已作用。而涉于不好。则人心便是人欲矣。如何。
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违。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韝。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
西山真氏如火如泉。未易充广之说。辑要以为虽可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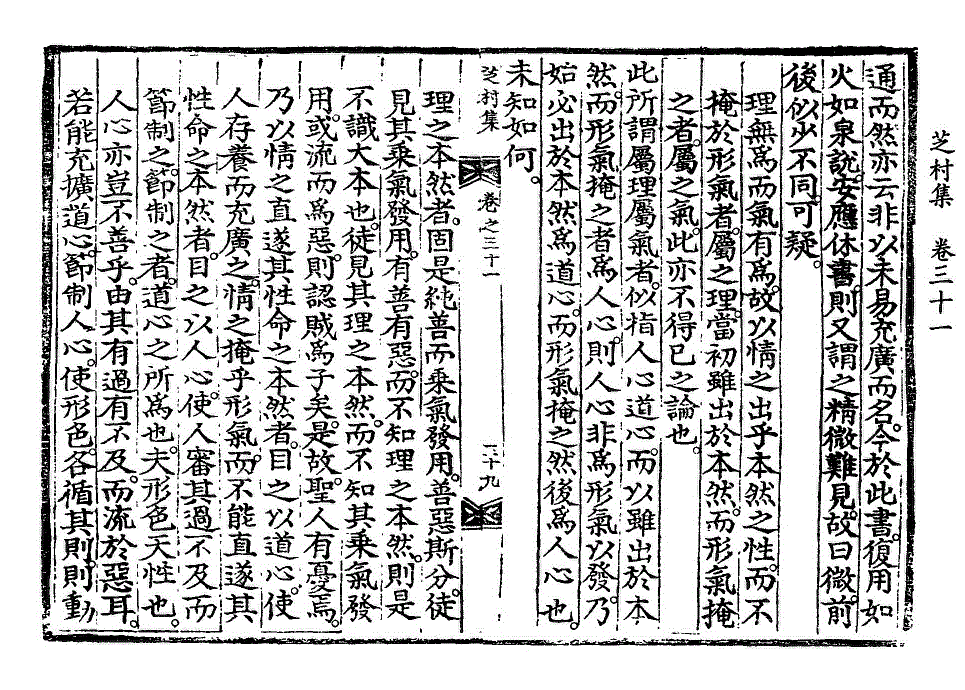 通而然亦云非以未易充广而名。今于此书。复用如火如泉说。安应休书。则又谓之精微难见。故曰微。前后似少不同。可疑。
通而然亦云非以未易充广而名。今于此书。复用如火如泉说。安应休书。则又谓之精微难见。故曰微。前后似少不同。可疑。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
此所谓属理属气者。似指人心道心。而以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为人心。则人心非为形气以发。乃始必出于本然为道心。而形气掩之然后为人心也。未知如何。
理之本然者。固是纯善而乘气发用。善恶斯分。徒见其乘气发用。有善有恶。而不知理之本然。则是不识大本也。徒见其理之本然。而不知其乘气发用。或流而为恶。则认贼为子矣。是故。圣人有忧焉。乃以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使人存养而充广之。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使人审其过不及而节制之。节制之者。道心之所为也。夫形色天性也。人心亦岂不善乎。由其有过有不及。而流于恶耳。若能充扩道心。节制人心。使形色。各循其则。则动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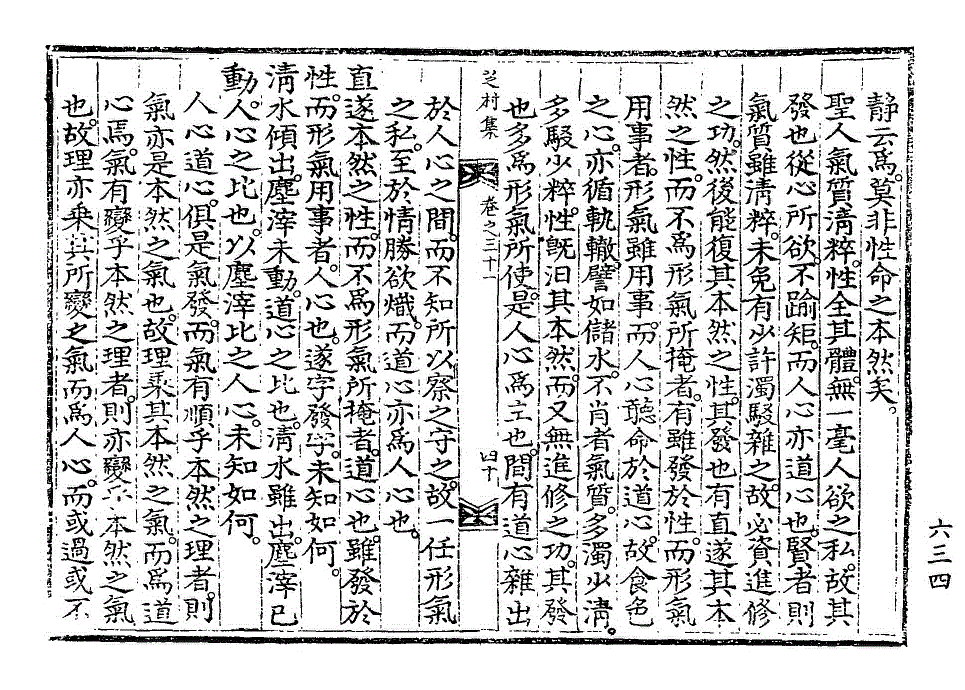 静云为。莫非性命之本然矣。
静云为。莫非性命之本然矣。圣人气质清粹。性全其体。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其发也从心所欲。不踰矩。而人心亦道心也。贤者则气质虽清粹。未免有少许浊驳杂之。故必资进修之功。然后能复其本然之性。其发也有直遂其本然之性。而不为形气所掩者。有虽发于性。而形气用事者。形气虽用事。而人心听命于道心。故食色之心。亦循轨辙。譬如储水。不肖者气质。多浊少清。多驳少粹。性既汩其本然。而又无进修之功。其发也多为形气所使。是人心为主也。间有道心杂出于人心之间。而不知所以察之守之。故一任形气之私。至于情胜欲炽。而道心亦为人心也。
直遂本然之性。而不为形气所掩者。道心也。虽发于性。而形气用事者。人心也。遂字发字。未知如何。
清水倾出。尘滓未动。道心之比也。清水虽出。尘滓已动。人心之比也。以尘滓比之人心。未知如何。
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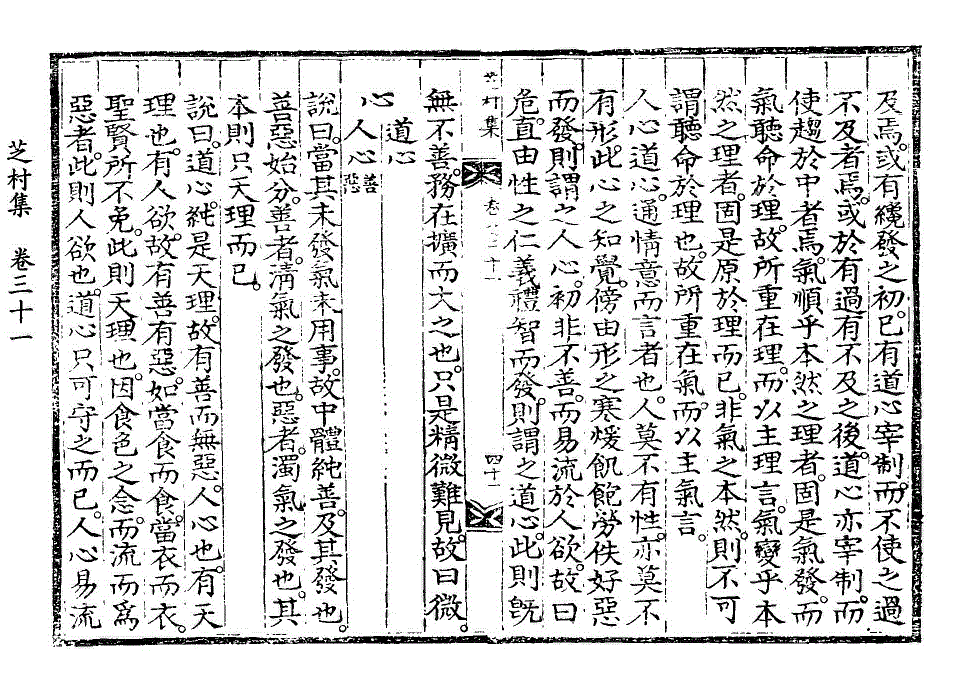 及焉。或有才发之初。已有道心宰制。而不使之过不及者焉。或于有过有不及之后。道心亦宰制。而使趋于中者焉。气顺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气发。而气听命于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主气言。
及焉。或有才发之初。已有道心宰制。而不使之过不及者焉。或于有过有不及之后。道心亦宰制。而使趋于中者焉。气顺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气发。而气听命于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主气言。人心道心。通情意而言者也。人莫不有性。亦莫不有形。此心之知觉。傍由形之寒煖饥饱劳佚好恶而发。则谓之人心。初非不善。而易流于人欲。故曰危。直由性之仁义礼智而发。则谓之道心。此则既无不善。务在扩而大之也。只是精微难见。故曰微。
心道心
人心(善恶)
说曰。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
说曰。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如当食而食。当衣而衣。圣贤所不免。此则天理也。因食色之念。而流而为恶者。此则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6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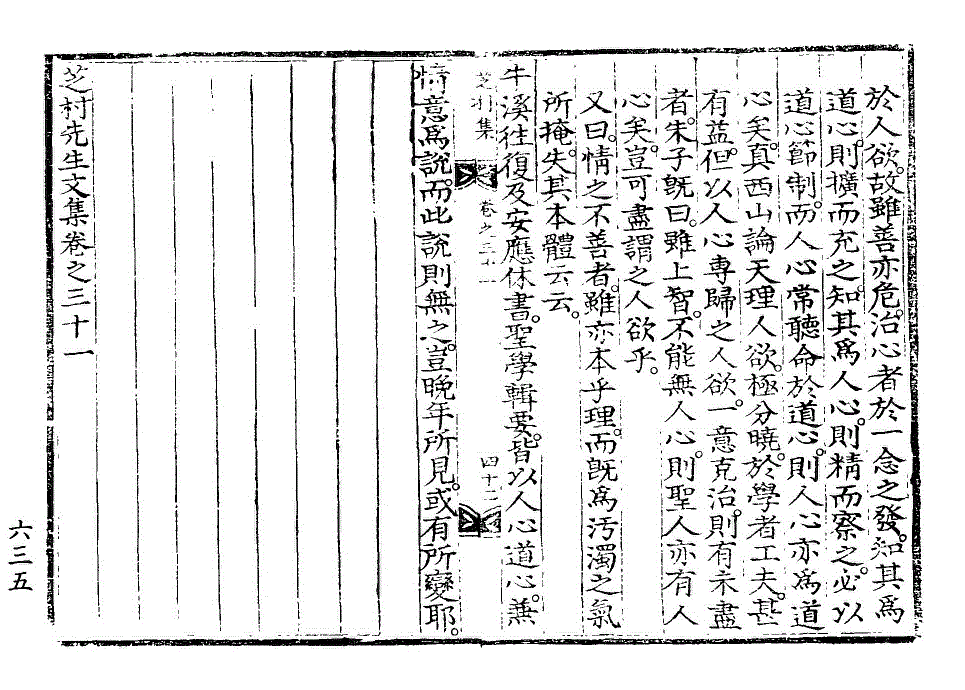 于人欲。故虽善亦危。治心者于一念之发。知其为道心。则扩而充之。知其为人心。则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常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亦为道心矣。真西山论天理人欲。极分晓。于学者工夫。甚有益。但以人心专归之人欲。一意克治。则有未尽者。朱子既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亦有人心矣。岂可尽谓之人欲乎。
于人欲。故虽善亦危。治心者于一念之发。知其为道心。则扩而充之。知其为人心。则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常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亦为道心矣。真西山论天理人欲。极分晓。于学者工夫。甚有益。但以人心专归之人欲。一意克治。则有未尽者。朱子既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亦有人心矣。岂可尽谓之人欲乎。又曰。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气所掩。失其本体云云。
牛溪往复及安应休书。圣学辑要。皆以人心道心。兼情意为说。而此说则无之。岂晚年所见。或有所变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