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x 页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杂记
杂记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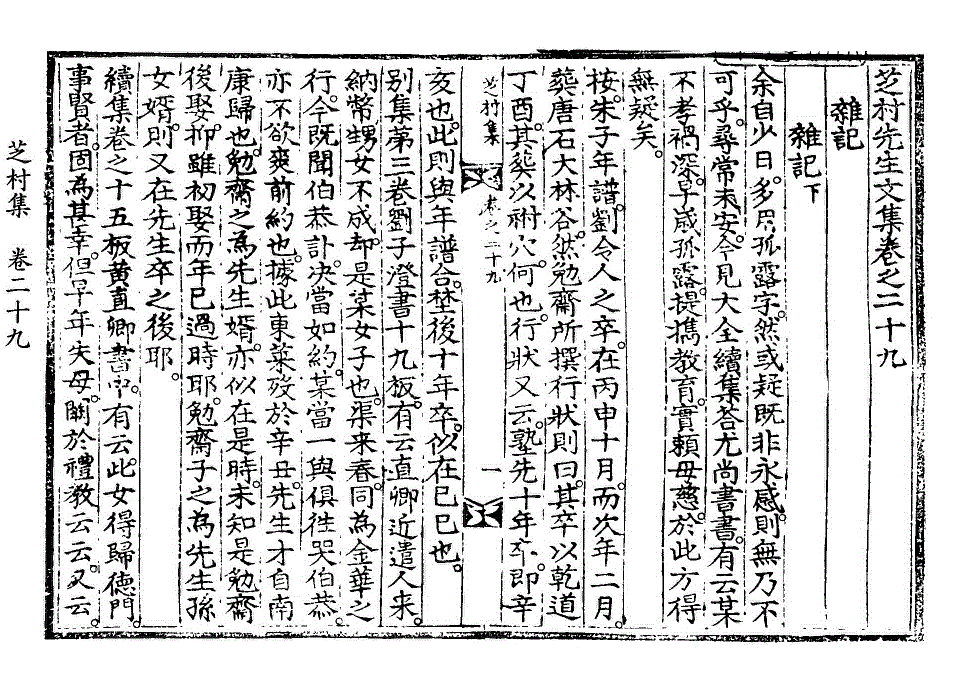 杂记(下)
杂记(下)余自少日。多用孤露字。然或疑既非永感。则无乃不可乎。寻常未安。今见大全续集答尤尚书书。有云某不孝祸深。早岁孤露。提携教育。实赖母慈。于此方得无疑矣。
按。朱子年谱。刘令人之卒。在丙申十月。而次年二月。葬唐石大林谷。然勉斋所撰行状则曰。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祔穴。何也。行状又云。塾先十年卒。即辛亥也。此则与年谱合。野后十年卒。似在己巳也。
别集第三卷刘子澄书十九板。有云直卿近遣人来。纳币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来春。同为金华之行。今既闻伯恭讣。决当如约。某当一与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约也。据此东莱殁于辛丑。先生才自南康归也。勉斋之为先生婿。亦似在是时。未知是勉斋后娶。抑虽初娶而年已过时耶。勉斋子之为先生孙女婿。则又在先生卒之后耶。
续集卷之十五板黄直卿书中。有云。此女得归德门。事贤者。固为甚幸。但早年失母。阙于礼教云云。又云。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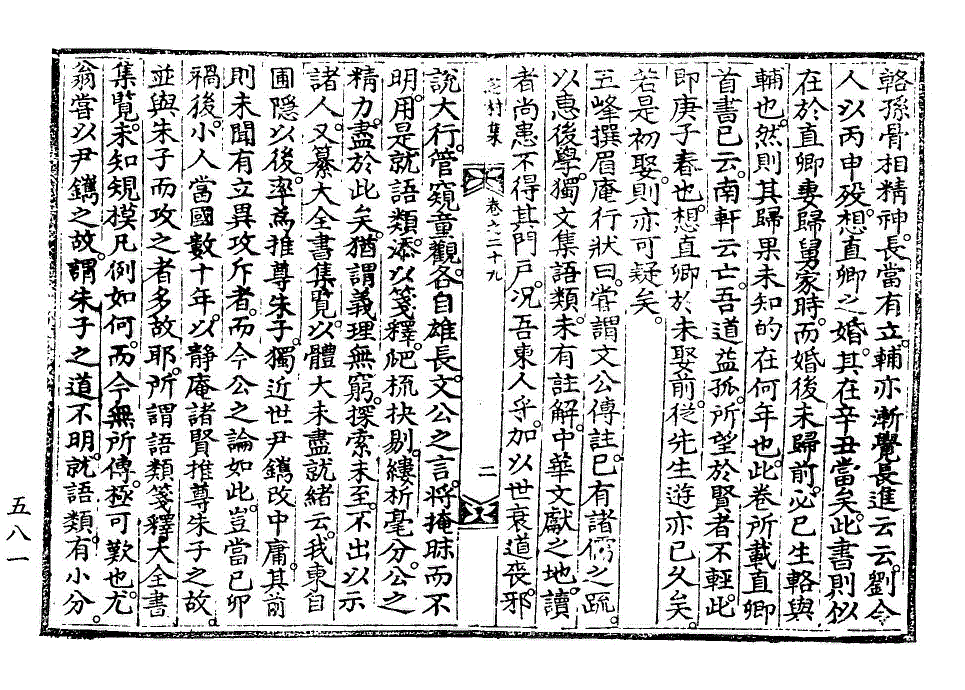 辂孙骨相精神。长当有立。辅亦渐觉长进云云。刘令人以丙申殁。想直卿之婚。其在辛丑当矣。此书则似在于直卿妻归舅家时。而婚后未归前。必已生辂与辅也。然则其归果未知的在何年也。此卷所载直卿首书已云。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所望于贤者不轻。此即庚子春也。想直卿于未娶前。从先生游亦已久矣。若是初娶。则亦可疑矣。
辂孙骨相精神。长当有立。辅亦渐觉长进云云。刘令人以丙申殁。想直卿之婚。其在辛丑当矣。此书则似在于直卿妻归舅家时。而婚后未归前。必已生辂与辅也。然则其归果未知的在何年也。此卷所载直卿首书已云。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所望于贤者不轻。此即庚子春也。想直卿于未娶前。从先生游亦已久矣。若是初娶。则亦可疑矣。五峰撰眉庵行状曰。尝谓文公传注。已有诸儒之疏。以惠后学。独文集语类。未有注解。中华文献之地。读者尚患不得其门户。况吾东人乎。加以世衰道丧。邪说大行。管窥童观。各自雄长。文公之言。将掩昧而不明。用是就语类。添以笺释。爬梳抉剔。缕析毫分。公之精力。尽于此矣。犹谓义理无穷。探索未至。不出以示诸人。又纂大全书集览。以体大未尽就绪云。我东自圃隐以后。率为推尊朱子。独近世尹鑴改中庸。其前则未闻有立异攻斥者。而今公之论如此。岂当己卯祸后。小人当国数十年。以静庵诸贤推尊朱子之故。并与朱子而攻之者多故耶。所谓语类笺释,大全书集览。未知规模凡例如何。而今无所传。极可叹也。尤翁尝以尹鑴之故。谓朱子之道不明。就语类。有小分。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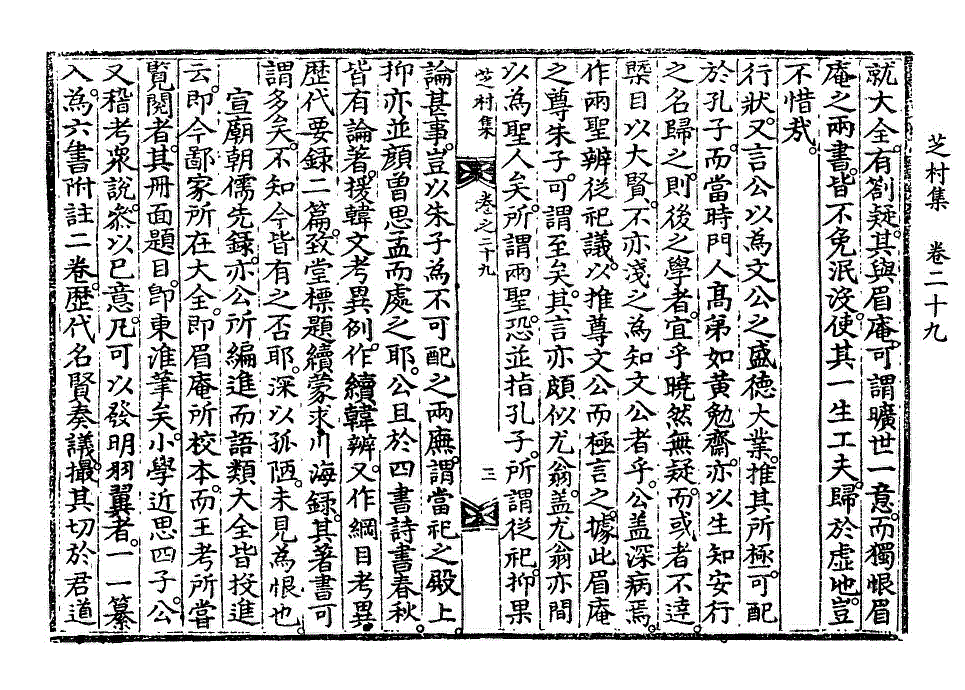 就大全。有劄疑。其与眉庵。可谓旷世一意。而独恨眉庵之两书。皆不免泯没。使其一生工夫。归于虚地。岂不惜哉。
就大全。有劄疑。其与眉庵。可谓旷世一意。而独恨眉庵之两书。皆不免泯没。使其一生工夫。归于虚地。岂不惜哉。行状。又言公以为文公之盛德大业。推其所极。可配于孔子。而当时门人高弟如黄勉斋。亦以生知安行之名归之。则后之学者。宜乎晓然无疑。而或者不达。槩目以大贤。不亦浅之为知文公者乎。公盖深病焉。作两圣辨从祀议。以推尊文公而极言之。据此眉庵之尊朱子。可谓至矣。其言亦颇似尤翁。盖尤翁亦间以为圣人矣。所谓两圣。恐并指孔子。所谓从祀。抑果论甚事。岂以朱子为不可配之两庑。谓当祀之殿上。抑亦并颜曾思孟而处之耶。公且于四书诗书春秋。皆有论著。援韩文考异例。作续韩辨。又作纲目考异,历代要录二篇。致堂标题,续蒙求,川海录。其著书可谓多矣。不知今皆有之否耶。深以孤陋。未见为恨也。 宣庙朝儒先录。亦公所编进而语类大全皆投进云。即今鄙家所在大全。即眉庵所校本。而王考所尝览阅者。其册面题目。即东淮笔矣。小学近思四子。公又稽考众说。参以己意。凡可以发明羽翼者。一一纂入。为六书附注二卷。历代名贤奏议。撮其切于君道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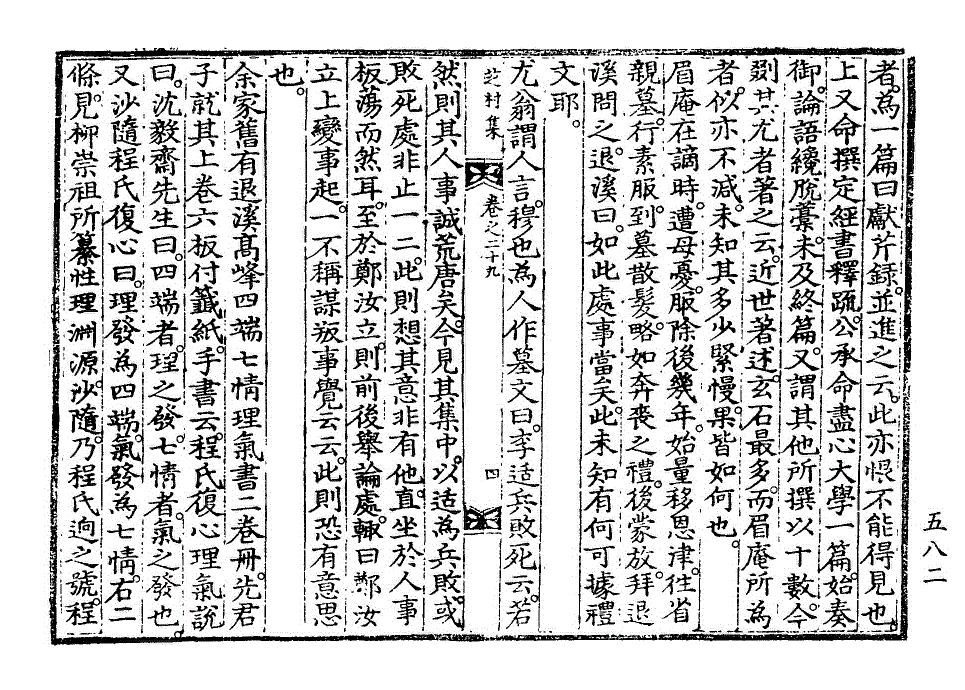 者。为一篇曰献芹录。并进之云。此亦恨不能得见也。上又命撰定经书释疏。公承命尽心大学一篇。始奏御。论语才脱藁。未及终篇。又谓其他所撰以十数。今剟其尤者著之云。近世著述。玄石最多。而眉庵所为者。似亦不减。未知其多少紧慢。果皆如何也。
者。为一篇曰献芹录。并进之云。此亦恨不能得见也。上又命撰定经书释疏。公承命尽心大学一篇。始奏御。论语才脱藁。未及终篇。又谓其他所撰以十数。今剟其尤者著之云。近世著述。玄石最多。而眉庵所为者。似亦不减。未知其多少紧慢。果皆如何也。眉庵在谪时。遭母忧。服除后几年。始量移恩津。往省亲墓。行素服。到墓散发。略如奔丧之礼。后蒙放。拜退溪问之。退溪曰。如此处事当矣。此未知有何可据礼文耶。
尤翁谓人言。穆也为人作墓文曰。李适兵败死云。若然则其人事诚荒唐矣。今见其集中。以适为兵败。或败死处非止一二。此则想其意非有他。直坐于人事板荡而然耳。至于郑汝立。则前后举论处。辄曰郑汝立上变事起。一不称谋叛事觉云云。此则恐有意思也。
余家旧有退溪高峰四端七情理气书二卷册。先君子就其上卷六板付签纸。手书云。程氏复心理气说曰。沈毅斋先生曰。四端者。理之发。七情者。气之发也。又沙随程氏复心曰。理发为四端。气发为七情。右二条。见柳崇祖所纂性理渊源。沙随。乃程氏迥之号。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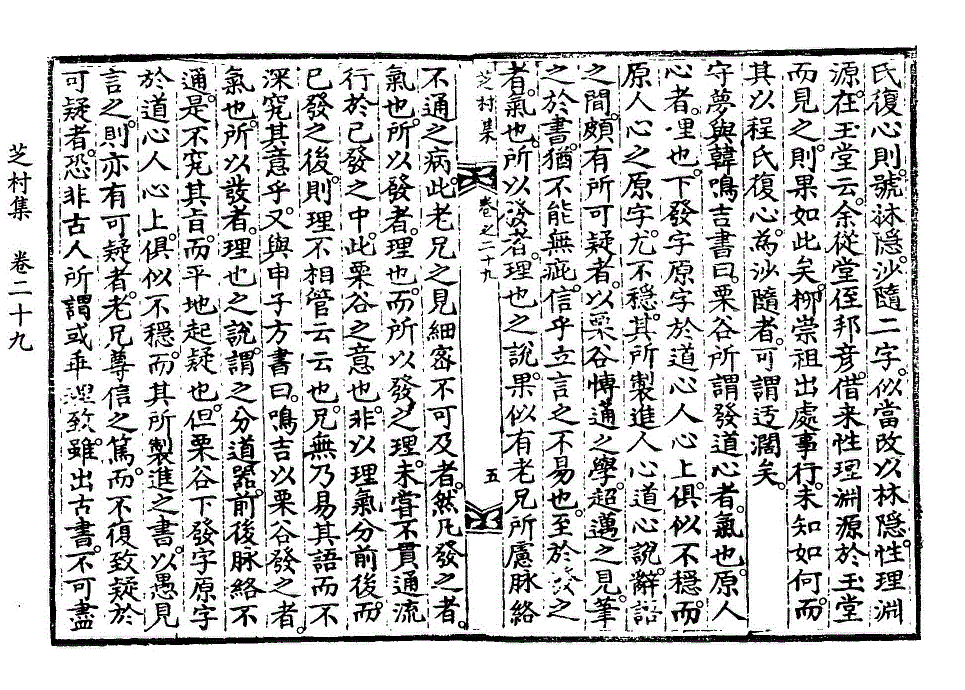 氏复心则。号林隐。沙随二字。似当改以林隐。性理渊源。在玉堂云。余从堂侄邦彦。借来性理渊源于玉堂而见之。则果如此矣。柳崇祖出处事行。未知如何。而其以程氏复心。为沙随者。可谓迂阔矣。
氏复心则。号林隐。沙随二字。似当改以林隐。性理渊源。在玉堂云。余从堂侄邦彦。借来性理渊源于玉堂而见之。则果如此矣。柳崇祖出处事行。未知如何。而其以程氏复心。为沙随者。可谓迂阔矣。守梦与韩鸣吉书曰。栗谷所谓发道心者。气也。原人心者。理也。下发字原字于道心人心上。俱似不稳。而原人心之原字。尤不稳。其所制进人心道心说。辞语之间。颇有所可疑者。以栗谷博通之学。超迈之见。笔之于书。犹不能无疵。信乎立言之不易也。至于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之说。果似有老兄所虑脉络不通之病。此老兄之见细密不可及者。然凡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而所以发之理。未尝不贯通流行于已发之中。此栗谷之意也。非以理气分前后。而已发之后。则理不相管云云也。兄无乃易其语而不深究其意乎。又与申子方书曰。鸣吉以栗谷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之说。谓之分道器。前后脉络不通。是不究其旨。而平地起疑也。但栗谷下发字原字于道心人心上。俱似不稳。而其所制进之书。以愚见言之。则亦有可疑者。老兄尊信之笃。而不复致疑于可疑者。恐非古人所谓或乖理致。虽出古书。不可尽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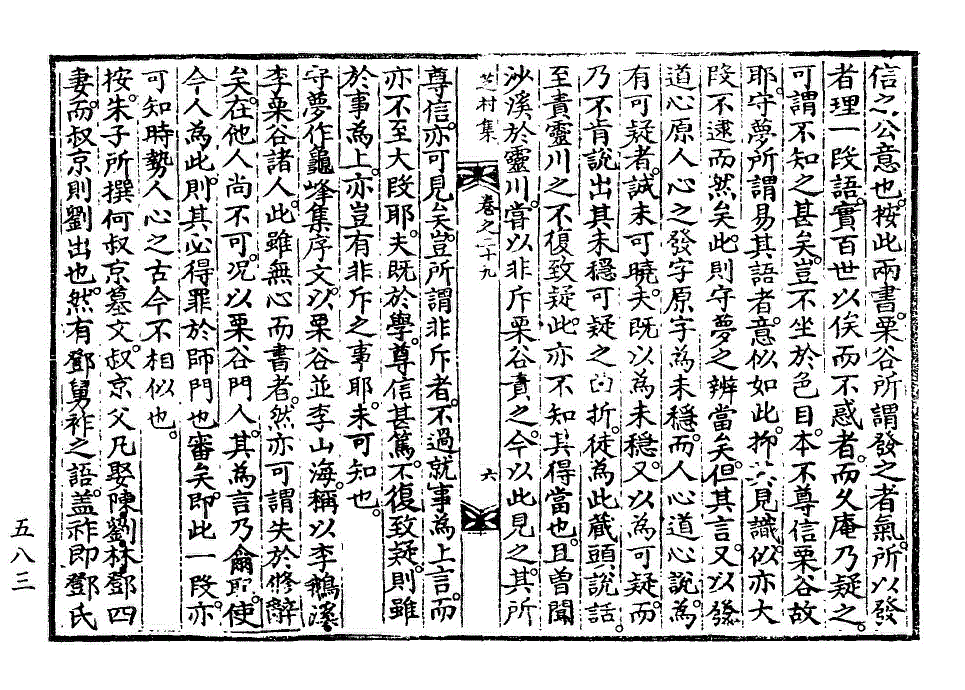 信之公意也。按此两书。栗谷所谓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一段语。实百世以俟而不惑者。而久庵乃疑之。可谓不知之甚矣。岂不坐于色目。本不尊信栗谷故耶。守梦所谓易其语者。意似如此。抑其见识。似亦大段不逮而然矣。此则守梦之辨当矣。但其言。又以发道心原人心之发字原字为未稳。而人心道心说。为有可疑者。诚未可晓。夫既以为未稳。又以为可疑。而乃不肯说出其未稳可疑之曲折。徒为此藏头说话。至责灵川之不复致疑。此亦不知其得当也。且曾闻沙溪于灵川。尝以非斥栗谷责之。今以此见之。其所尊信。亦可见矣。岂所谓非斥者。不过就事为上言。而亦不至大段耶。夫既于学。尊信甚笃。不复致疑。则虽于事为上。亦岂有非斥之事耶。未可知也。
信之公意也。按此两书。栗谷所谓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一段语。实百世以俟而不惑者。而久庵乃疑之。可谓不知之甚矣。岂不坐于色目。本不尊信栗谷故耶。守梦所谓易其语者。意似如此。抑其见识。似亦大段不逮而然矣。此则守梦之辨当矣。但其言。又以发道心原人心之发字原字为未稳。而人心道心说。为有可疑者。诚未可晓。夫既以为未稳。又以为可疑。而乃不肯说出其未稳可疑之曲折。徒为此藏头说话。至责灵川之不复致疑。此亦不知其得当也。且曾闻沙溪于灵川。尝以非斥栗谷责之。今以此见之。其所尊信。亦可见矣。岂所谓非斥者。不过就事为上言。而亦不至大段耶。夫既于学。尊信甚笃。不复致疑。则虽于事为上。亦岂有非斥之事耶。未可知也。守梦作龟峰集序文。以栗谷并李山海。称以李鹅溪,李栗谷诸人。此虽无心而书者。然亦可谓失于修辞矣。在他人尚不可。况以栗谷门人。其为言乃尔耶。使今人为此。则其必得罪于师门也审矣。即此一段。亦可知时势人心之古今不相似也。
按。朱子所撰何叔京墓文。叔京父凡娶陈,刘,林,邓四妻。而叔京则刘出也。然有邓舅祚之语。盖祚即邓氏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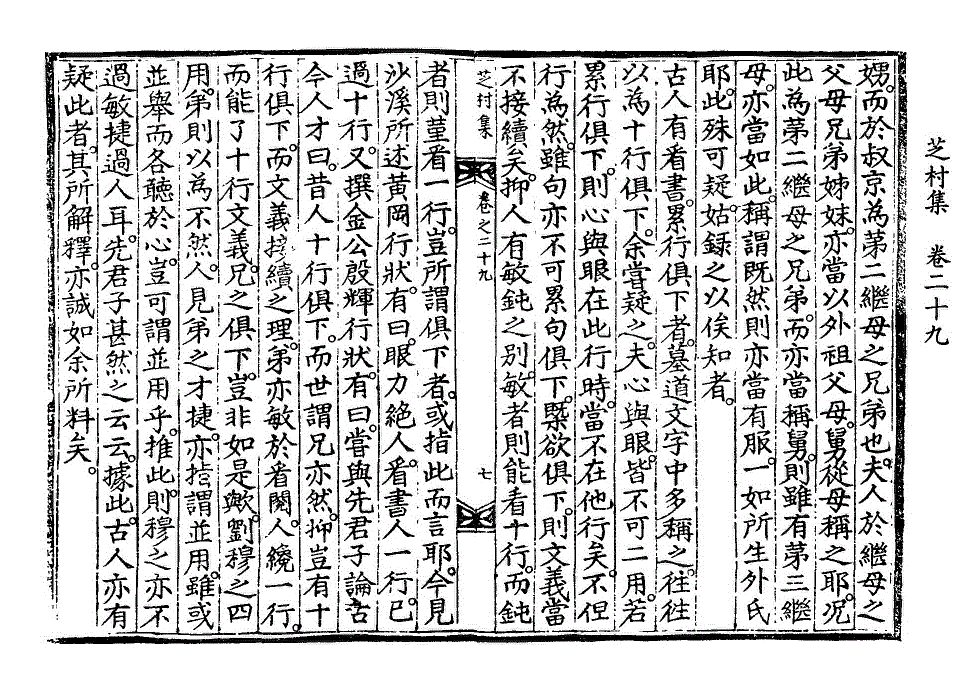 喃。而于叔京为第二继母之兄弟也。夫人于继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亦当以外祖父母。舅从母称之耶。况此为第二继母之兄弟。而亦当称舅。则虽有第三继母。亦当如此。称谓既然则亦当有服。一如所生外氏耶。此殊可疑。姑录之以俟知者。
喃。而于叔京为第二继母之兄弟也。夫人于继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亦当以外祖父母。舅从母称之耶。况此为第二继母之兄弟。而亦当称舅。则虽有第三继母。亦当如此。称谓既然则亦当有服。一如所生外氏耶。此殊可疑。姑录之以俟知者。古人有看书。累行俱下者。墓道文字中多称之。往往以为十行俱下。余尝疑之。夫心与眼。皆不可二用。若累行俱下。则心与眼在此行时。当不在他行矣。不但行为然。虽句亦不可累句俱下。槩欲俱下。则文义当不接续矣。抑人有敏钝之别。敏者则能看十行。而钝者则堇看一行。岂所谓俱下者。或指此而言耶。今见沙溪所述黄冈行状。有曰。眼力绝人。看书人一行。已过十行。又撰金公殷辉行状。有曰。尝与先君子论古今人才曰。昔人十行俱下。而世谓兄亦然。抑岂有十行俱下。而文义接续之理。弟亦敏于看阅。人才一行。而能了十行文义。兄之俱下。岂非如是欤。刘穆之四用。弟则以为不然。人见弟之才捷。亦指谓并用。虽或并举而各听于心。岂可谓并用乎。推此。则穆之亦不过敏捷过人耳。先君子甚然之云云。据此。古人亦有疑此者。其所解释。亦诚如余所料矣。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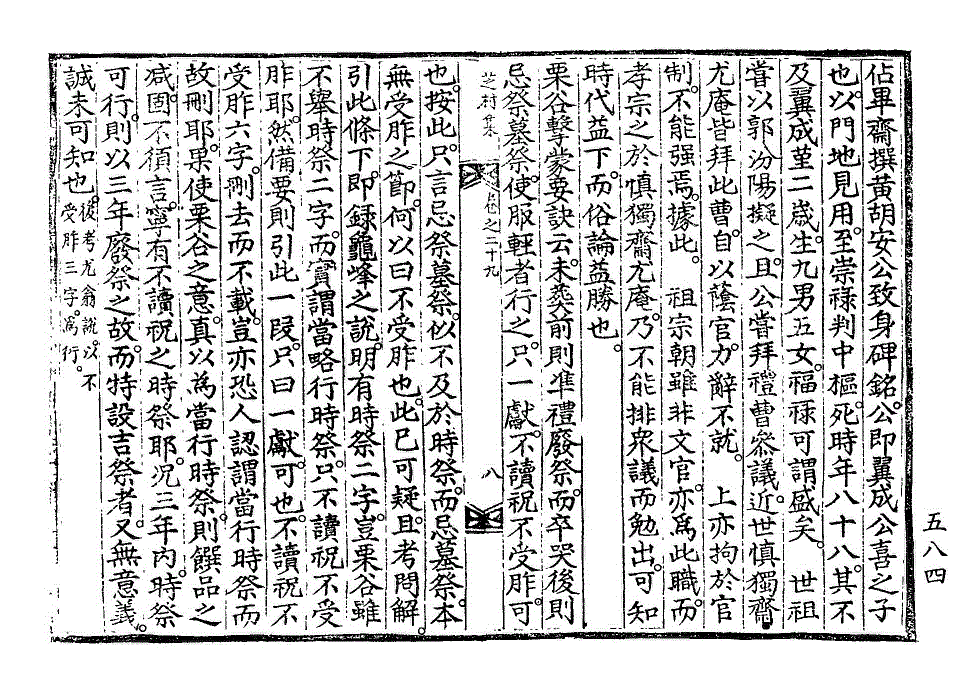 佔毕斋撰黄胡安公致身碑铭。公即翼成公喜之子也。以门地见用。至崇禄判中枢。死时年八十八。其不及翼成堇二岁。生九男五女。福禄可谓盛矣。 世祖尝以郭汾阳拟之。且公尝拜礼曹参议。近世慎独斋,尤庵皆拜此曹。自以荫官。力辞不就。 上亦拘于官制。不能强焉。据此。 祖宗朝虽非文官。亦为此职。而孝宗之于慎独斋尤庵。乃不能排众议而勉出。可知时代益下。而俗论益胜也。
佔毕斋撰黄胡安公致身碑铭。公即翼成公喜之子也。以门地见用。至崇禄判中枢。死时年八十八。其不及翼成堇二岁。生九男五女。福禄可谓盛矣。 世祖尝以郭汾阳拟之。且公尝拜礼曹参议。近世慎独斋,尤庵皆拜此曹。自以荫官。力辞不就。 上亦拘于官制。不能强焉。据此。 祖宗朝虽非文官。亦为此职。而孝宗之于慎独斋尤庵。乃不能排众议而勉出。可知时代益下。而俗论益胜也。栗谷击蒙要诀云。未葬前则准礼废祭。而卒哭后则忌祭墓祭。使服轻者行之。只一献。不读祝不受胙。可也。按此。只言忌祭墓祭。似不及于时祭。而忌墓祭。本无受胙之节。何以曰不受胙也。此已可疑。且考问解。引此条下。即录龟峰之说。明有时祭二字。岂栗谷虽不举时祭二字。而实谓当略行时祭。只不读祝不受胙耶。然备要则引此一段。只曰一献。可也。不读祝不受胙六字。删去而不载。岂亦恐人认谓当行时祭而故删耶。果使栗谷之意。真以为当行时祭。则馔品之减。固不须言。宁有不读祝之时祭耶。况三年内。时祭可行。则以三年废祭之故。而特设吉祭者。又无意义。诚未可知也。(后考尤翁说。以不受胙三字。为衍。)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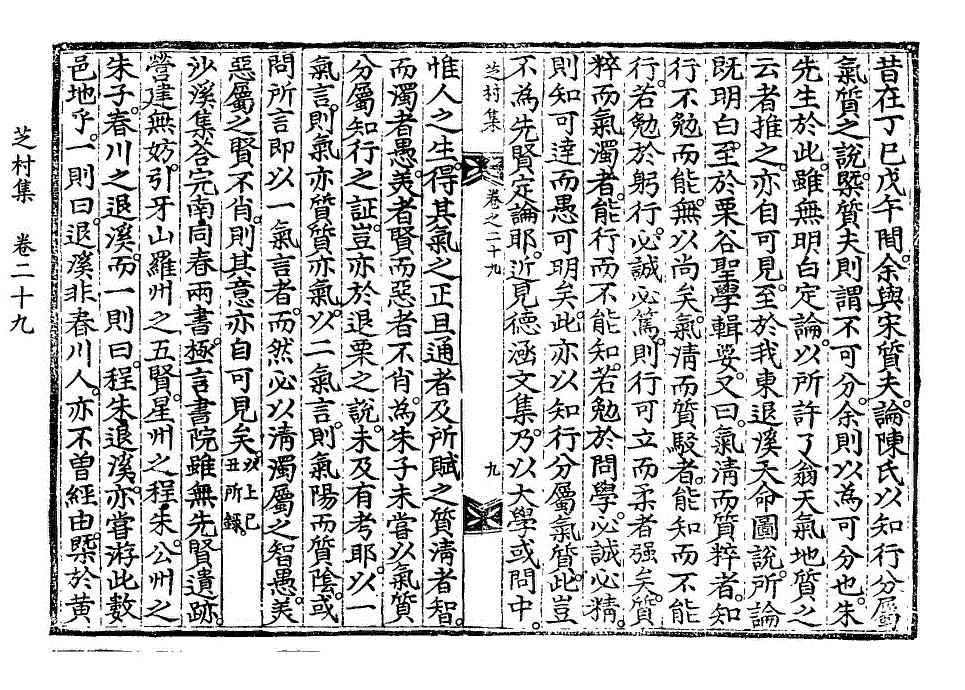 昔在丁巳戊午间。余与宋质夫。论陈氏以知行分属气质之说。槩质夫则谓不可分。余则以为可分也。朱先生于此。虽无明白定论。以所许了翁天气地质之云者推之。亦自可见。至于我东退溪天命图说。所论既明白。至于栗谷圣学辑要。又曰。气清而质粹者。知行不勉而能。无以尚矣。气清而质驳者。能知而不能行。若勉于躬行。必诚必笃。则行可立而柔者强矣。质粹而气浊者。能行而不能知。若勉于问学。必诚必精。则知可达而愚可明矣。此亦以知行分属气质。此岂不为先贤定论耶。近见德涵文集。乃以大学或问中。惟人之生。得其气之正且通者及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为朱子未尝以气质分属知行之证。岂亦于退栗之说。未及有考耶。以一气言。则气亦质质亦气。以二气言。则气阳而质阴。或问所言即以一气言者。而然必以清浊属之智愚。美恶属之贤不肖。则其意亦自可见矣。(以上己丑所录。)
昔在丁巳戊午间。余与宋质夫。论陈氏以知行分属气质之说。槩质夫则谓不可分。余则以为可分也。朱先生于此。虽无明白定论。以所许了翁天气地质之云者推之。亦自可见。至于我东退溪天命图说。所论既明白。至于栗谷圣学辑要。又曰。气清而质粹者。知行不勉而能。无以尚矣。气清而质驳者。能知而不能行。若勉于躬行。必诚必笃。则行可立而柔者强矣。质粹而气浊者。能行而不能知。若勉于问学。必诚必精。则知可达而愚可明矣。此亦以知行分属气质。此岂不为先贤定论耶。近见德涵文集。乃以大学或问中。惟人之生。得其气之正且通者及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为朱子未尝以气质分属知行之证。岂亦于退栗之说。未及有考耶。以一气言。则气亦质质亦气。以二气言。则气阳而质阴。或问所言即以一气言者。而然必以清浊属之智愚。美恶属之贤不肖。则其意亦自可见矣。(以上己丑所录。)沙溪集答完南,同春两书。极言书院虽无先贤遗迹。营建无妨。引牙山罗州之五贤。星州之程,朱。公州之朱子。春川之退溪。而一则曰。程朱,退溪。亦尝游此数邑地乎。一则曰。退溪非春川人。亦不曾经由。槩于黄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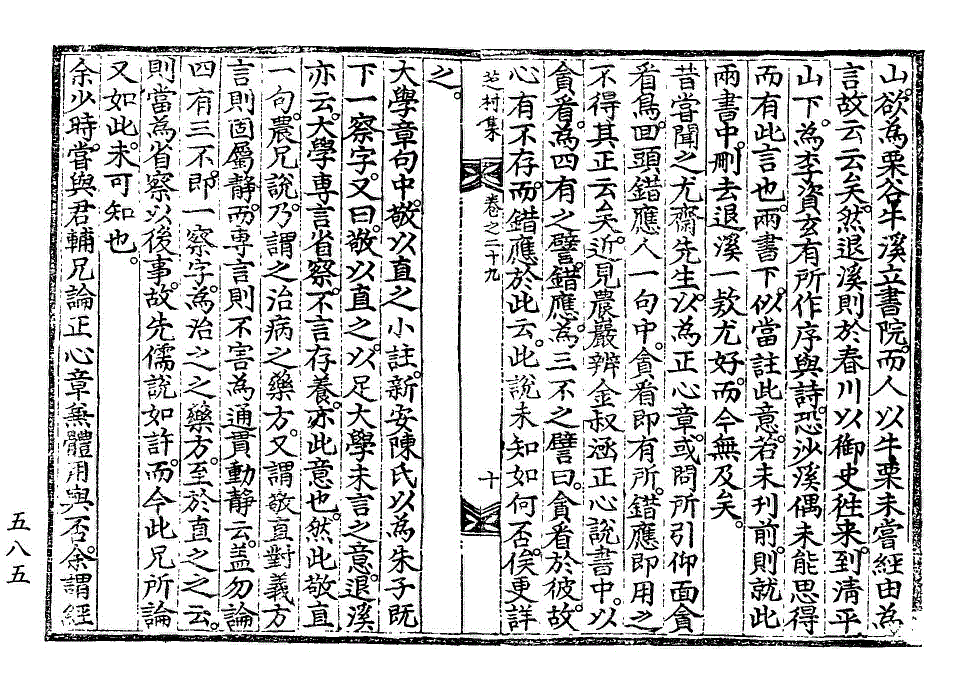 山。欲为栗谷,牛溪立书院。而人以牛,栗未尝经由为言故云云矣。然退溪则于春川以御史往来。到清平山下。为李资玄有所作序与诗。恐沙溪偶未能思得而有此言也。两书下。似当注此意。若未刊前。则就此两书中。删去退溪一款尤好。而今无及矣。
山。欲为栗谷,牛溪立书院。而人以牛,栗未尝经由为言故云云矣。然退溪则于春川以御史往来。到清平山下。为李资玄有所作序与诗。恐沙溪偶未能思得而有此言也。两书下。似当注此意。若未刊前。则就此两书中。删去退溪一款尤好。而今无及矣。昔尝闻之尤斋先生。以为正心章。或问所引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一句中。贪看即有所。错应即用之不得其正云矣。近见农岩辨金叔涵正心说书中。以贪看。为四有之譬。错应。为三不之譬曰。贪看于彼。故心有不存。而错应于此云。此说未知如何否。俟更详之。
大学章句中。敬以直之小注。新安陈氏以为朱子既下一察字。又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学未言之意。退溪亦云。大学专言省察。不言存养。亦此意也。然此敬直一句。农兄说。乃谓之治病之药方。又谓敬直对义方言则固属静。而专言则不害为通贯动静云。盖勿论四有三不。即一察字。为治之之药方。至于直之之云。则当为省察以后事。故先儒说如许。而今此兄所论又如此。未可知也。
余少时。尝与君辅兄论正心章兼体用与否。余谓经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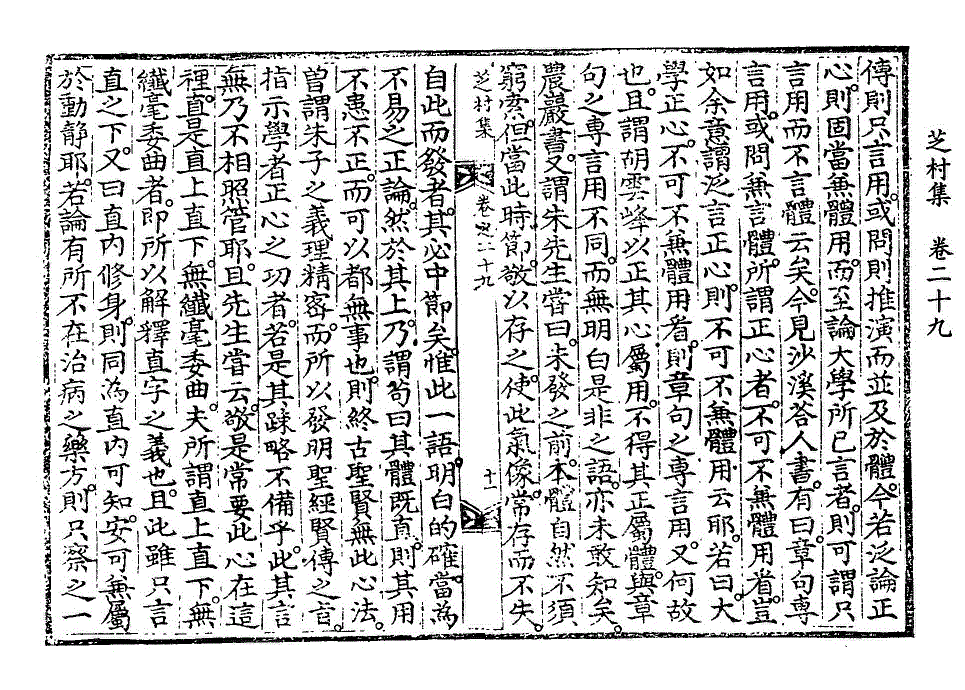 传则只言用。或问则推演而并及于体。今若泛论正心。则固当兼体用。而至论大学所已言者。则可谓只言用而不言体云矣。今见沙溪答人书。有曰。章句专言用。或问兼言体。所谓正心者。不可不兼体用看。岂如余意谓泛言正心。则不可不兼体用云耶。若曰。大学正心。不可不兼体用看。则章句之专言用。又何故也。且谓胡云峰以正其心属用。不得其正属体。与章句之专言用不同。而无明白是非之语。亦未敢知矣。农岩书。又谓朱先生尝曰。未发之前。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此时节。敬以存之。使此气像。常存而不失。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惟此一语。明白的确。当为不易之正论。然于其上。乃谓苟曰其体既直。则其用不患不正。而可以都无事也。则终古圣贤无此心法。曾谓朱子之义理精密。而所以发明圣经贤传之旨。指示学者正心之功者。若是其疏略不备乎。此其言无乃不相照管耶。且先生尝云。敬是常要此心在这里。直是直上直下。无纤毫委曲。夫所谓直上直下。无纤毫委曲者。即所以解释直字之义也。且此虽只言直之下。又曰直内修身。则同为直内可知。安可兼属于动静耶。若论有所不在治病之药方。则只察之一
传则只言用。或问则推演而并及于体。今若泛论正心。则固当兼体用。而至论大学所已言者。则可谓只言用而不言体云矣。今见沙溪答人书。有曰。章句专言用。或问兼言体。所谓正心者。不可不兼体用看。岂如余意谓泛言正心。则不可不兼体用云耶。若曰。大学正心。不可不兼体用看。则章句之专言用。又何故也。且谓胡云峰以正其心属用。不得其正属体。与章句之专言用不同。而无明白是非之语。亦未敢知矣。农岩书。又谓朱先生尝曰。未发之前。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此时节。敬以存之。使此气像。常存而不失。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惟此一语。明白的确。当为不易之正论。然于其上。乃谓苟曰其体既直。则其用不患不正。而可以都无事也。则终古圣贤无此心法。曾谓朱子之义理精密。而所以发明圣经贤传之旨。指示学者正心之功者。若是其疏略不备乎。此其言无乃不相照管耶。且先生尝云。敬是常要此心在这里。直是直上直下。无纤毫委曲。夫所谓直上直下。无纤毫委曲者。即所以解释直字之义也。且此虽只言直之下。又曰直内修身。则同为直内可知。安可兼属于动静耶。若论有所不在治病之药方。则只察之一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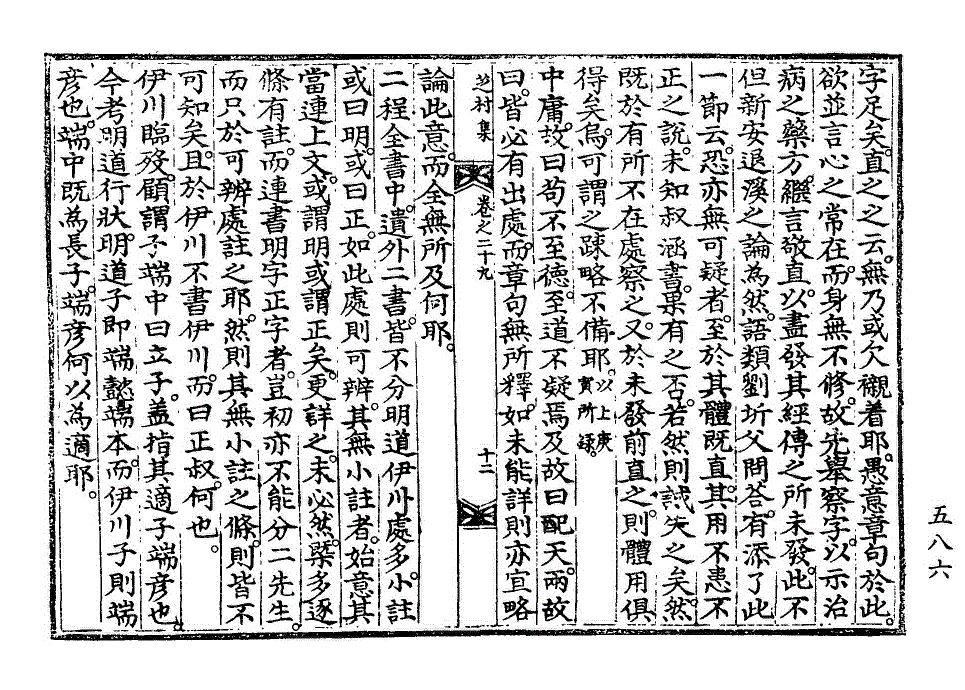 字足矣。直之之云。无乃或欠衬着耶。愚意章句于此。欲并言心之常在。而身无不修。故先举察字。以示治病之药方。继言敬直。以尽发其经传之所未发。此不但新安退溪之论为然。语类刘圻父问答。有添了此一节云。恐亦无可疑者。至于其体既直。其用不患不正之说。未知叔涵书。果有之否。若然则诚失之矣。然既于有所不在处察之。又于未发前直之。则体用俱得矣。乌可谓之疏略不备耶。(以上庚寅所录。)
字足矣。直之之云。无乃或欠衬着耶。愚意章句于此。欲并言心之常在。而身无不修。故先举察字。以示治病之药方。继言敬直。以尽发其经传之所未发。此不但新安退溪之论为然。语类刘圻父问答。有添了此一节云。恐亦无可疑者。至于其体既直。其用不患不正之说。未知叔涵书。果有之否。若然则诚失之矣。然既于有所不在处察之。又于未发前直之。则体用俱得矣。乌可谓之疏略不备耶。(以上庚寅所录。)中庸。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及故曰配天。两故曰。皆必有出处。而章句无所释。如未能详则亦宜略论此意。而全无所及何耶。
二程全书中。遗外二书。皆不分明道伊川处多。小注或曰明。或曰正。如此处则可辨。其无小注者。始意其当连上文。或谓明或谓正矣。更详之。未必然。槩多逐条有注。而连书明字正字者。岂初亦不能分二先生。而只于可辨处注之耶。然则其无小注之条。则皆不可知矣。且于伊川不书伊川。而曰正叔。何也。
伊川临殁。顾谓子端中曰立子。盖指其适子端彦也。今考明道行状。明道子即端懿,端本。而伊川子则端彦也。端中既为长子。端彦何以为适耶。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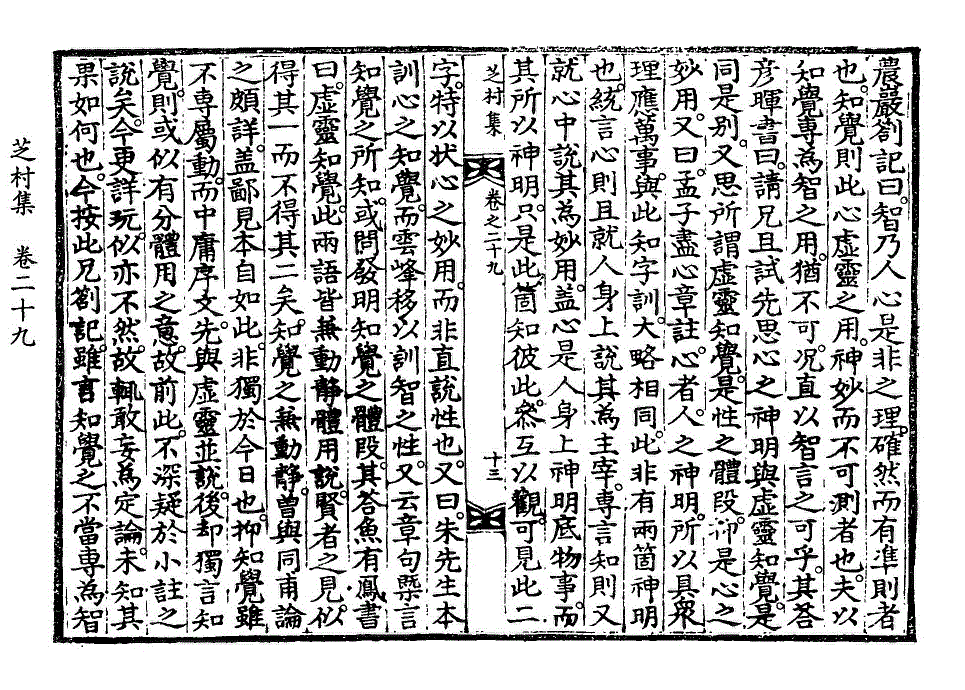 农岩劄记曰。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确然而有准则者也。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夫以知觉专为智之用。犹不可。况直以智言之可乎。其答彦晖书曰。请兄且试先思心之神明与虚灵知觉。是同是别。又思所谓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又曰。孟子尽心章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与此知字训。大略相同。此非有两个神明也。统言心则且就人身上说其为主宰。专言知则又就心中说其为妙用。盖心是人身上神明底物事。而其所以神明。只是此个知彼此。参互以观。可见此二字。特以状心之妙用。而非直说性也。又曰。朱先生本训心之知觉。而云峰移以训智之性。又云章句槩言知觉之所知。或问发明知觉之体段。其答鱼有凤书曰。虚灵知觉。此两语皆兼动静体用说。贤者之见。似得其一而不得其二矣。知觉之兼动静。曾与同甫论之颇详。盖鄙见本自如此。非独于今日也。抑知觉虽不专属动。而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则或似有分体用之意。故前此。不深疑于小注之说矣。今更详玩。似亦不然。故辄敢妄为定论。未知其果如何也。今按此兄劄记。虽言知觉之不当专为智
农岩劄记曰。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确然而有准则者也。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夫以知觉专为智之用。犹不可。况直以智言之可乎。其答彦晖书曰。请兄且试先思心之神明与虚灵知觉。是同是别。又思所谓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又曰。孟子尽心章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与此知字训。大略相同。此非有两个神明也。统言心则且就人身上说其为主宰。专言知则又就心中说其为妙用。盖心是人身上神明底物事。而其所以神明。只是此个知彼此。参互以观。可见此二字。特以状心之妙用。而非直说性也。又曰。朱先生本训心之知觉。而云峰移以训智之性。又云章句槩言知觉之所知。或问发明知觉之体段。其答鱼有凤书曰。虚灵知觉。此两语皆兼动静体用说。贤者之见。似得其一而不得其二矣。知觉之兼动静。曾与同甫论之颇详。盖鄙见本自如此。非独于今日也。抑知觉虽不专属动。而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则或似有分体用之意。故前此。不深疑于小注之说矣。今更详玩。似亦不然。故辄敢妄为定论。未知其果如何也。今按此兄劄记。虽言知觉之不当专为智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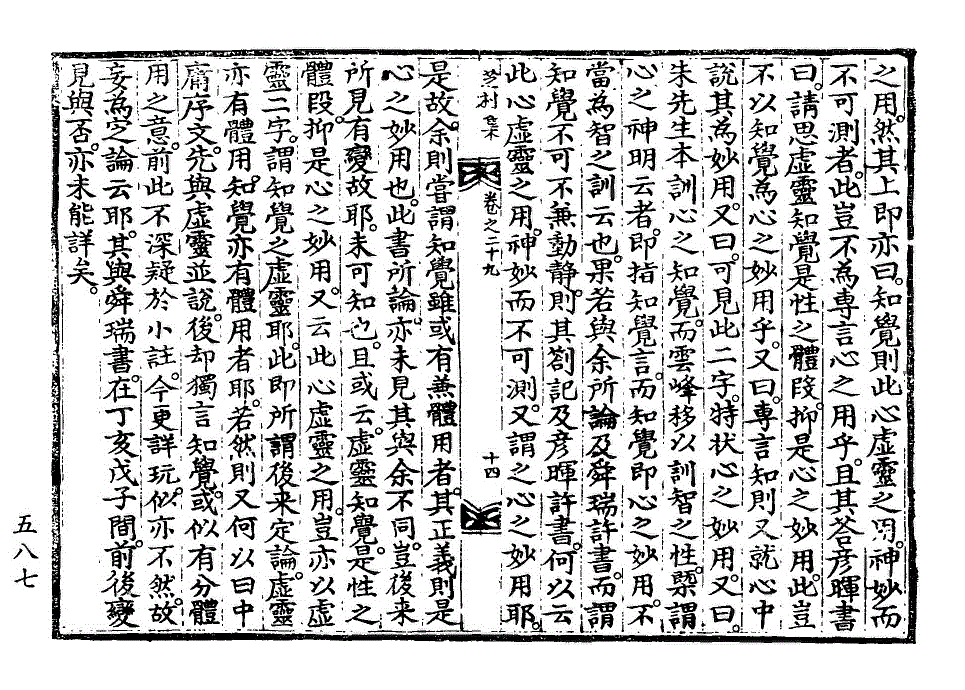 之用。然其上即亦曰。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此岂不为专言心之用乎。且其答彦晖书曰。请思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此岂不以知觉为心之妙用乎。又曰。专言知则又就心中说其为妙用。又曰。可见此二字。特状心之妙用。又曰。朱先生本训心之知觉。而云峰移以训智之性。槩谓心之神明云者。即指知觉言。而知觉即心之妙用。不当为智之训云也。果若与余所论及舜瑞许书。而谓知觉不可不兼动静。则其劄记及彦晖许书。何以云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又谓之心之妙用耶。是故。余则尝谓知觉虽或有兼体用者。其正义则是心之妙用也。此书所论。亦未见其与余不同。岂后来所见有变故耶。未可知也。且或云。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又云此心虚灵之用。岂亦以虚灵二字。谓知觉之虚灵耶。此即所谓后来定论。虚灵亦有体用。知觉亦有体用者耶。若然则又何以曰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或似有分体用之意。前此不深疑于小注。今更详玩。似亦不然。故妄为定论云耶。其与舜瑞书。在丁亥戊子间。前后变见与否。亦未能详矣。
之用。然其上即亦曰。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此岂不为专言心之用乎。且其答彦晖书曰。请思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此岂不以知觉为心之妙用乎。又曰。专言知则又就心中说其为妙用。又曰。可见此二字。特状心之妙用。又曰。朱先生本训心之知觉。而云峰移以训智之性。槩谓心之神明云者。即指知觉言。而知觉即心之妙用。不当为智之训云也。果若与余所论及舜瑞许书。而谓知觉不可不兼动静。则其劄记及彦晖许书。何以云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又谓之心之妙用耶。是故。余则尝谓知觉虽或有兼体用者。其正义则是心之妙用也。此书所论。亦未见其与余不同。岂后来所见有变故耶。未可知也。且或云。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又云此心虚灵之用。岂亦以虚灵二字。谓知觉之虚灵耶。此即所谓后来定论。虚灵亦有体用。知觉亦有体用者耶。若然则又何以曰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或似有分体用之意。前此不深疑于小注。今更详玩。似亦不然。故妄为定论云耶。其与舜瑞书。在丁亥戊子间。前后变见与否。亦未能详矣。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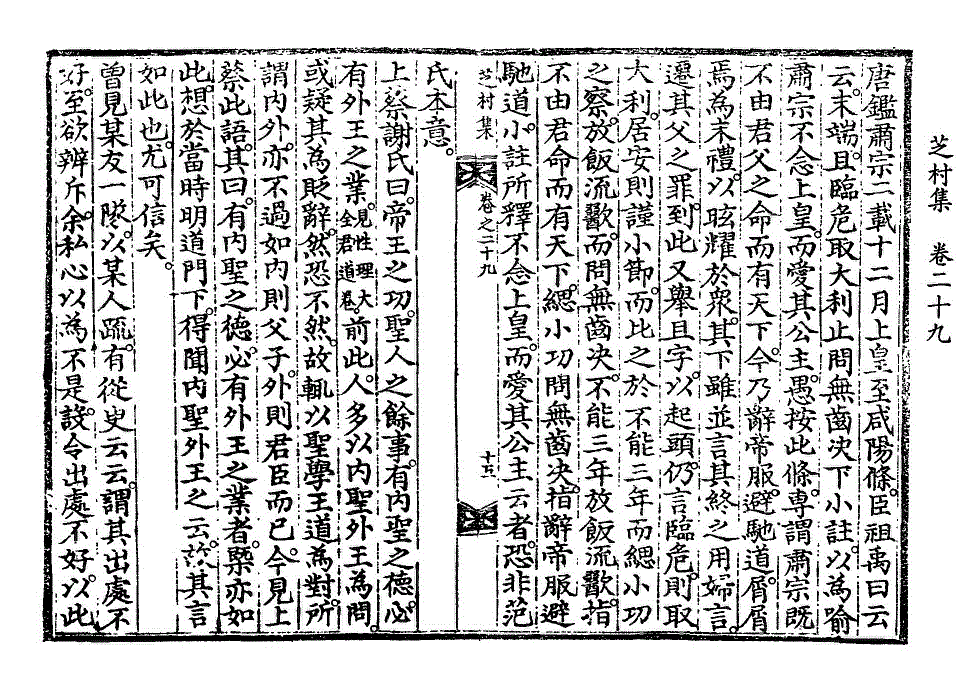 唐鉴肃宗二载十二月上皇至咸阳条。臣祖禹曰云云。末端。且临危取大利止问无齿决下小注。以为喻肃宗不念上皇。而爱其公主。愚按此条。专谓肃宗既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今乃辞帝服。避驰道。屑屑焉为末礼。以昡耀于众。其下虽并言其终之用妇言。迁其父之罪。到此又举且字。以起头。仍言临危。则取大利。居安则谨小节。而比之于不能三年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不能三年放饭流歠。指不由君命而有天下。缌小功问无齿决。指辞帝服避驰道。小注所释不念上皇。而爱其公主云者。恐非范氏本意。
唐鉴肃宗二载十二月上皇至咸阳条。臣祖禹曰云云。末端。且临危取大利止问无齿决下小注。以为喻肃宗不念上皇。而爱其公主。愚按此条。专谓肃宗既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今乃辞帝服。避驰道。屑屑焉为末礼。以昡耀于众。其下虽并言其终之用妇言。迁其父之罪。到此又举且字。以起头。仍言临危。则取大利。居安则谨小节。而比之于不能三年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不能三年放饭流歠。指不由君命而有天下。缌小功问无齿决。指辞帝服避驰道。小注所释不念上皇。而爱其公主云者。恐非范氏本意。上蔡谢氏曰。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有内圣之德。必有外王之业。(见性理大全君道卷。)前此。人多以内圣外王为问。或疑其为贬辞。然恐不然。故辄以圣学王道为对。所谓内外。亦不过如内则父子。外则君臣而已。今见上蔡此语。其曰。有内圣之德。必有外王之业者。槩亦如此。想于当时明道门下。得闻内圣外王之云。故其言如此也。尤可信矣。
曾见某友一队。以某人疏。有从臾云云。谓其出处不好。至欲辨斥。余私心以为不是。设令出处不好。以此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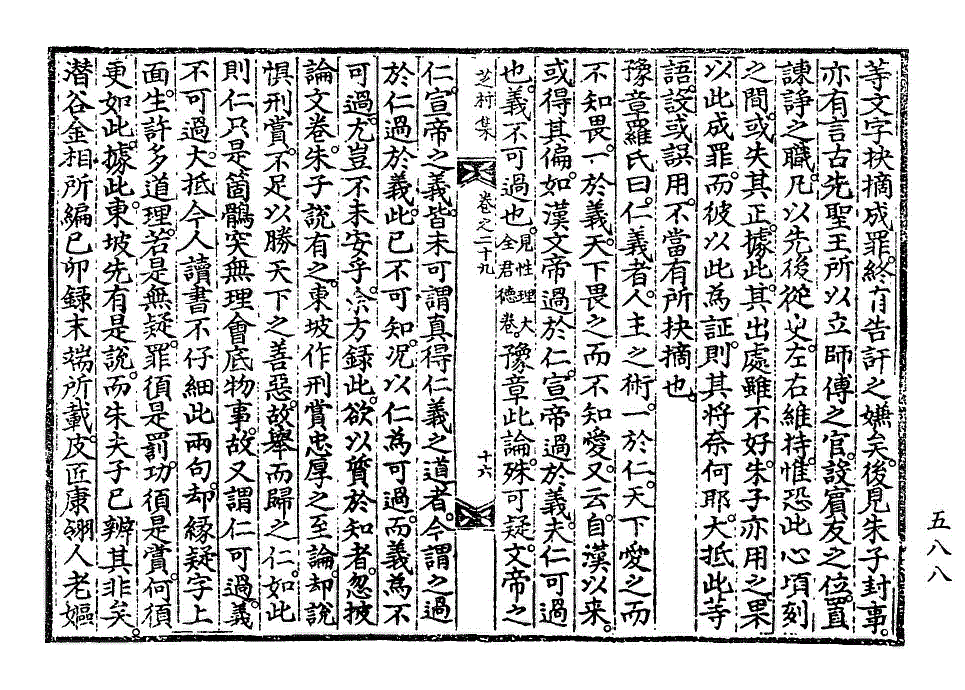 等文字抉摘成罪。终有告讦之嫌矣。后见朱子封事。亦有言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从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据此。其出处虽不好。朱子亦用之。果以此成罪。而彼以此为证。则其将奈何耶。大抵此等语。设或误用。不当有所抉摘也。
等文字抉摘成罪。终有告讦之嫌矣。后见朱子封事。亦有言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从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据此。其出处虽不好。朱子亦用之。果以此成罪。而彼以此为证。则其将奈何耶。大抵此等语。设或误用。不当有所抉摘也。豫章罗氏曰。仁义者。人主之术。一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于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又云。自汉以来。或得其偏。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夫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见性理大全君德卷。)豫章此论。殊可疑。文帝之仁。宣帝之义。皆未可谓真得仁义之道者。今谓之过于仁过于义。此已不可知。况以仁为可过。而义为不可过。尤岂不未安乎。余方录此。欲以质于知者。忽披论文卷。朱子说有之。东坡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却说惧刑赏。不足以胜天下之善恶。故举而归之仁。如此则仁只是个鹘突无理会底物事。故又谓仁可过。义不可过。大抵今人读书不仔细此两句。却缘疑字上面。生许多道理。若是无疑。罪须是罚。功须是赏。何须更如此。据此。东坡先有是说。而朱夫子已辨其非矣。潜谷金相所编己卯录末端所载。皮匠康翎人老妪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9H 页
 三件事中。二件有可疑者。夫皮匠中。设有隐君子韬光而晦彩者。静庵果就而问学。则其非隐君子审矣。况至于共宿。则宁有不知其姓名之理耶。此已可疑。且当静庵之赐死也。其弟崇祖。必闻其命。而及先生未死而奔往也。虽其心罔极。然与奔父母丧者不同。何乃哭于路傍耶。且此其行必在命下之初。虽士大夫在乡者。必未及得闻。彼山谷间老妪。安能有闻耶。且静庵虽大贤人。伤痛而泣涕则当矣。至于哭则必不然。盖以事理推之。似皆如此。不知潜谷于何得闻而有此所记。无乃皆各有苗脉。而就学哀哭等语。或出于传说之稍过者耶。
三件事中。二件有可疑者。夫皮匠中。设有隐君子韬光而晦彩者。静庵果就而问学。则其非隐君子审矣。况至于共宿。则宁有不知其姓名之理耶。此已可疑。且当静庵之赐死也。其弟崇祖。必闻其命。而及先生未死而奔往也。虽其心罔极。然与奔父母丧者不同。何乃哭于路傍耶。且此其行必在命下之初。虽士大夫在乡者。必未及得闻。彼山谷间老妪。安能有闻耶。且静庵虽大贤人。伤痛而泣涕则当矣。至于哭则必不然。盖以事理推之。似皆如此。不知潜谷于何得闻而有此所记。无乃皆各有苗脉。而就学哀哭等语。或出于传说之稍过者耶。朱子答滕德粹书。有曰。释氏之说。易以惑人。诚如来喻。然如所谓若有所喜。则已是中其毒矣。据此。若有所喜四字。似德粹书中语。则已以下即先生语也。尤翁尝以美村之于黑水。谓之中毒者非一。至丁卯疏亦用之。玄石书。力言中毒之不衬。谓必传其道守其学。思欲易天下。然后可谓之中毒。其时余欲以朱子此书。奉质而未及。可叹。盖中毒。亦有浅深。若其深者。固如玄石所云。乃若浅者。虽略有所好。已不可谓不中毒矣。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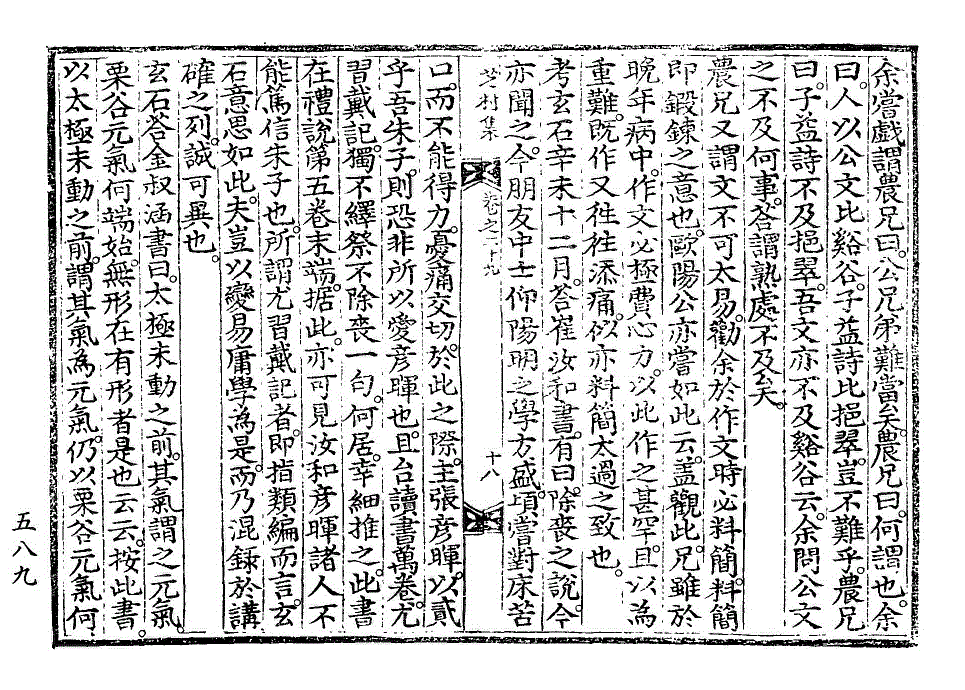 余尝戏谓农兄曰。公兄弟难当矣。农兄曰。何谓也。余曰。人以公文比溪谷。子益诗比挹翠。岂不难乎。农兄曰。子益诗不及挹翠。吾文亦不及溪谷云。余问公文之不及何事。答谓熟处不及矣。
余尝戏谓农兄曰。公兄弟难当矣。农兄曰。何谓也。余曰。人以公文比溪谷。子益诗比挹翠。岂不难乎。农兄曰。子益诗不及挹翠。吾文亦不及溪谷云。余问公文之不及何事。答谓熟处不及矣。农兄又谓文不可太易。劝余于作文时必料简。料简即锻鍊之意也。欧阳公亦尝如此云。盖观此。兄虽于晚年病中。作文必极费心力。以此作之甚罕。且以为重难。既作又往往添痛。似亦料简太过之致也。
考玄石辛未十二月。答崔汝和书。有曰。除丧之说。今亦闻之。今朋友中士仰阳明之学方盛。顷尝对床苦口。而不能得力。忧痛交切。于此之际。主张彦晖。以贰乎吾朱子。则恐非所以爱彦晖也。且台读书万卷。尤习戴记。独不绎祭不除丧一句。何居。幸细推之。此书在礼说第五卷末端。据此。亦可见汝和彦晖诸人不能笃信朱子也。所谓尤习戴记者。即指类编而言。玄石意思如此。夫岂以变易庸学为是。而乃混录于讲确之列。诚可异也。
玄石答金叔涵书曰。太极未动之前。其气谓之元气。栗谷元气何端始。无形在有形者是也云云。按此书。以太极未动之前。谓其气为元气。仍以栗谷元气何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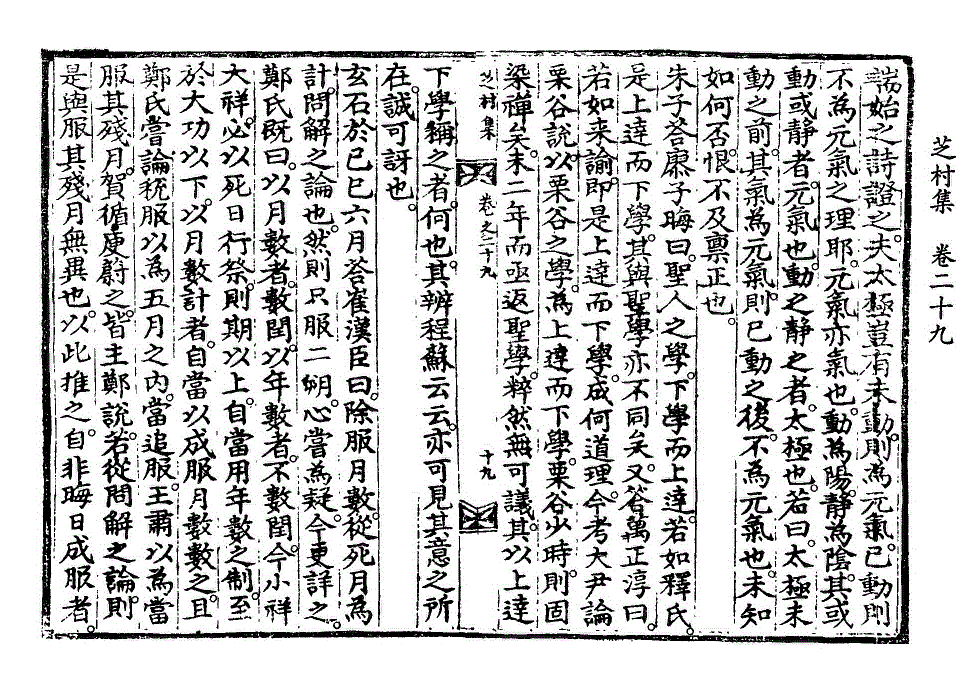 端始之诗證之。夫太极岂有未动。则为元气。已动则不为元气之理耶。元气亦气也。动为阳。静为阴。其或动或静者。元气也。动之静之者。太极也。若曰。太极未动之前。其气为元气。则已动之后。不为元气也。未知如何否。恨不及禀正也。
端始之诗證之。夫太极岂有未动。则为元气。已动则不为元气之理耶。元气亦气也。动为阳。静为阴。其或动或静者。元气也。动之静之者。太极也。若曰。太极未动之前。其气为元气。则已动之后。不为元气也。未知如何否。恨不及禀正也。朱子答廖子晦曰。圣人之学。下学而上达。若如释氏。是上达而下学。其与圣学亦不同矣。又答万正淳曰。若如来谕。即是上达而下学。成何道理。今考大尹论栗谷说。以栗谷之学。为上达而下学。栗谷少时。则固染禅矣。未二年而亟返圣学。粹然无可议。其以上达下学称之者。何也。其辨程苏云云。亦可见其意之所在。诚可讶也。
玄石于己巳六月答崔汉臣曰。除服月数。从死月为计。问解之论也。然则只服二朔。心尝为疑。今更详之。郑氏既曰。以月数者。数闰。以年数者。不数闰。今小祥大祥。必以死日行祭。则期以上。自当用年数之制。至于大功以下。以月数计者。自当以成服月数数之。且郑氏尝论税服以为五月之内。当追服。王肃以为当服其残月。贺循,庾蔚之。皆主郑说。若从问解之论。则是与服其残月无异也。以此推之。自非晦日成服者。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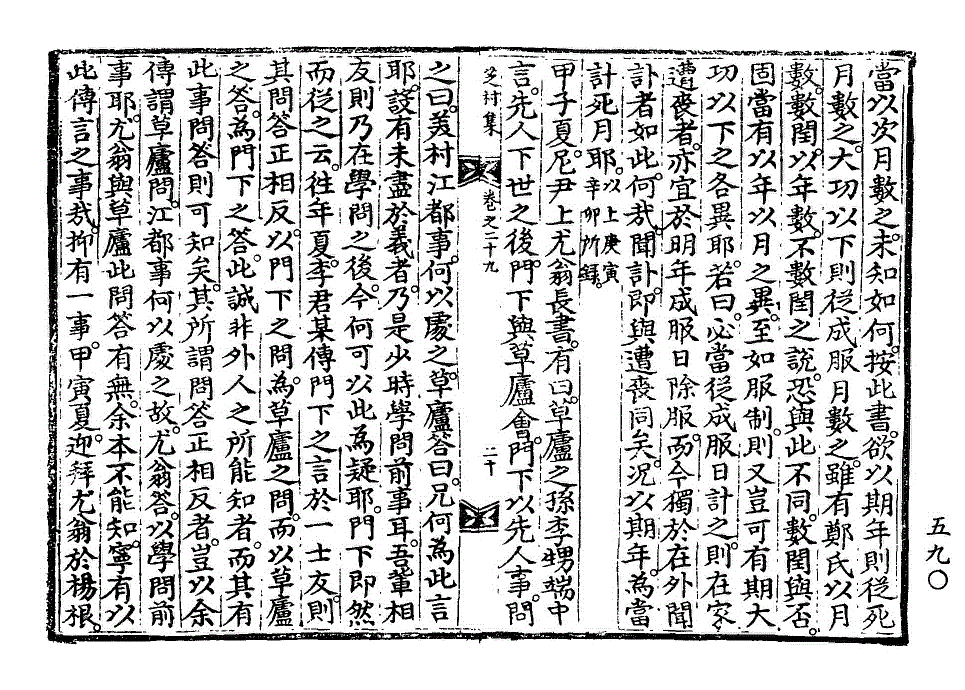 当以次月数之。未知如何。按此书。欲以期年则从死月数之。大功以下则从成服月数之。虽有郑氏以月数。数闰。以年数。不数闰之说。恐与此不同。数闰与否。固当有以年以月之异。至如服制。则又岂可有期大功以下之各异耶。若曰。必当从成服日计之。则在家遭丧者。亦宜于明年成服日除服。而今独于在外闻讣者如此。何哉。闻讣。即与遭丧同矣。况以期年。为当计死月耶。(以上庚寅辛卯所录。)
当以次月数之。未知如何。按此书。欲以期年则从死月数之。大功以下则从成服月数之。虽有郑氏以月数。数闰。以年数。不数闰之说。恐与此不同。数闰与否。固当有以年以月之异。至如服制。则又岂可有期大功以下之各异耶。若曰。必当从成服日计之。则在家遭丧者。亦宜于明年成服日除服。而今独于在外闻讣者如此。何哉。闻讣。即与遭丧同矣。况以期年。为当计死月耶。(以上庚寅辛卯所录。)甲子夏。尼尹上尤翁长书。有曰。草庐之孙李甥端中言。先人下世之后。门下与草庐会。门下以先人事。问之曰。美村江都事。何以处之。草庐答曰。兄何为此言耶。设有未尽于义者。乃是少时学问前事耳。吾辈相友则乃在学问之后。今何可以此为疑耶。门下即然而从之云。往年夏。李君某传门下之言于一士友。则其问答正相反。以门下之问。为草庐之问。而以草庐之答。为门下之答。此诚非外人之所能知者。而其有此事问答则可知矣。其所谓问答正相反者。岂以余传谓草庐问。江都事何以处之故。尤翁答。以学问前事耶。尤翁与草庐此问答有无。余本不能知。宁有以此传言之事哉。抑有一事。甲寅夏。迎拜尤翁于杨根。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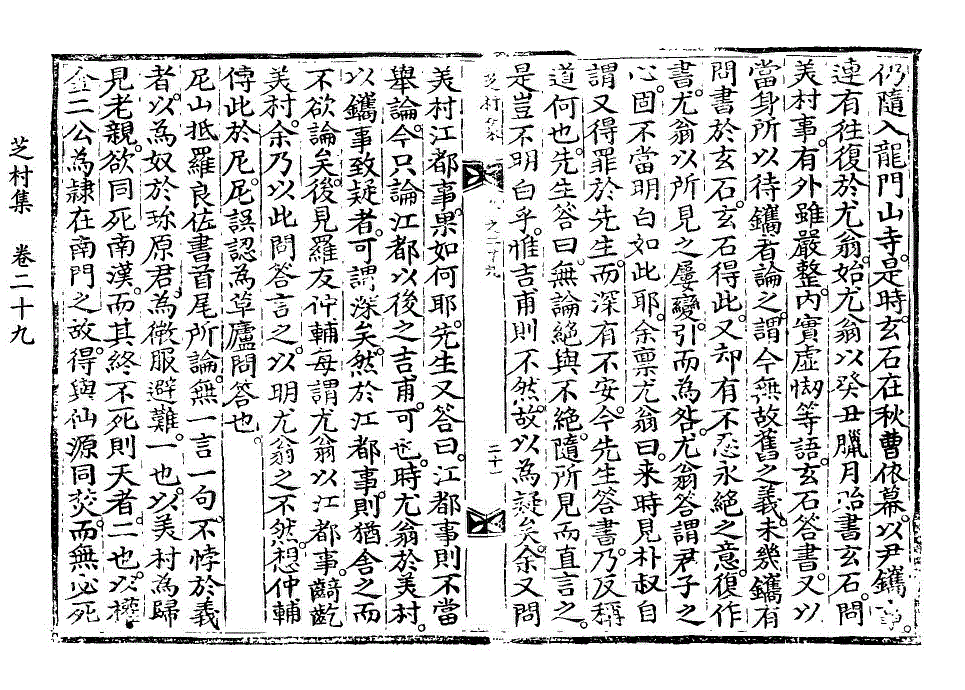 仍随入龙门山寺。是时。玄石在秋曹依幕。以尹鑴事。连有往复于尤翁。始尤翁以癸丑腊月贻书玄石。问美村事。有外虽严整。内实虚怯等语。玄石答书。又以当身所以待鑴者论之。谓今无故旧之义。未几鑴有问书于玄石。玄石得此。又却有不忍永绝之意。复作书。尤翁以所见之屡变。引而为咎。尤翁答谓君子之心。固不当明白如此耶。余禀尤翁曰。来时见朴叔自谓又得罪于先生。而深有不安。今先生答书。乃反称道何也。先生答曰。无论绝与不绝。随所见而直言之。是岂不明白乎。惟吉甫则不然。故以为疑矣。余又问美村江都事。果如何耶。先生又答曰。江都事则不当举论。今只论江都以后之吉甫。可也。时尤翁于美村。以鑴事致疑者。可谓深矣。然于江都事。则犹舍之而不欲论矣。后见罗友仲辅每谓尤翁以江都事。齮龁美村。余乃以此问答言之。以明尤翁之不然。想仲辅传此于尼。尼误认为草庐问答也。
仍随入龙门山寺。是时。玄石在秋曹依幕。以尹鑴事。连有往复于尤翁。始尤翁以癸丑腊月贻书玄石。问美村事。有外虽严整。内实虚怯等语。玄石答书。又以当身所以待鑴者论之。谓今无故旧之义。未几鑴有问书于玄石。玄石得此。又却有不忍永绝之意。复作书。尤翁以所见之屡变。引而为咎。尤翁答谓君子之心。固不当明白如此耶。余禀尤翁曰。来时见朴叔自谓又得罪于先生。而深有不安。今先生答书。乃反称道何也。先生答曰。无论绝与不绝。随所见而直言之。是岂不明白乎。惟吉甫则不然。故以为疑矣。余又问美村江都事。果如何耶。先生又答曰。江都事则不当举论。今只论江都以后之吉甫。可也。时尤翁于美村。以鑴事致疑者。可谓深矣。然于江都事。则犹舍之而不欲论矣。后见罗友仲辅每谓尤翁以江都事。齮龁美村。余乃以此问答言之。以明尤翁之不然。想仲辅传此于尼。尼误认为草庐问答也。尼山抵罗良佐书首尾所论。无一言一句。不悖于义者。以为奴于珍原君。为微服避难。一也。以美村为归见老亲。欲同死南汉。而其终不死则天者。二也。以权,金二公为隶在南门之故。得与仙源同焚。而无必死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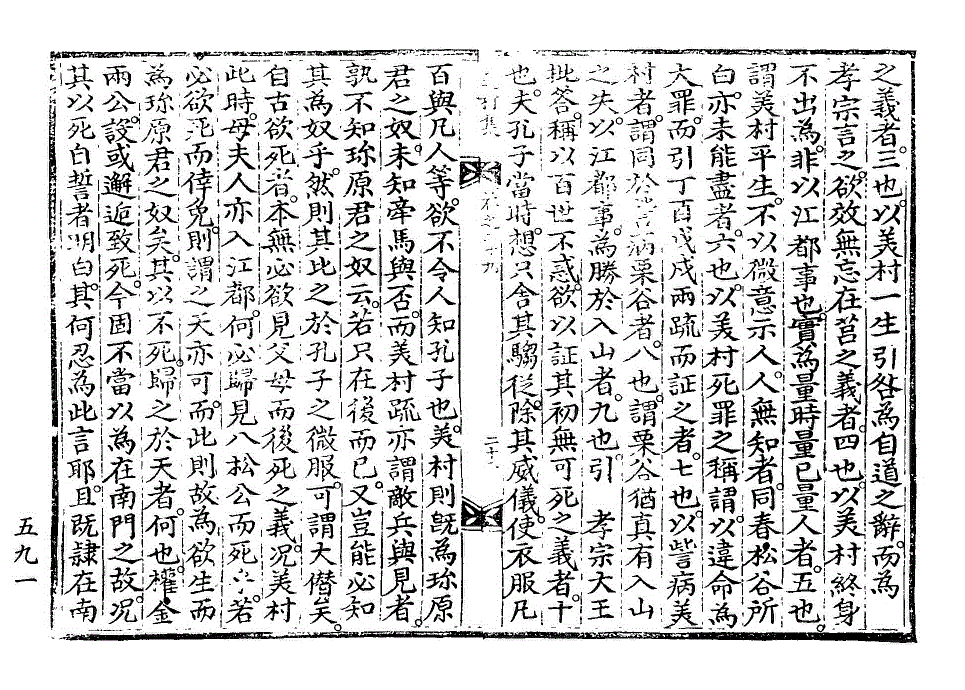 之义者。三也。以美村一生引咎为自道之辞。而为 孝宗言之。欲效无忘在莒之义者。四也。以美村终身不出为。非以江都事也。实为量时量己量人者。五也。谓美村平生。不以微意示人。人无知者。同春,松谷所白。亦未能尽者。六也。以美村死罪之称谓。以违命为大罪。而引丁酉戊戌两疏而证之者。七也。以訾病美村者。谓同于訾病栗谷者。八也。谓栗谷犹真有入山之失。以江都事。为胜于入山者。九也。引 孝宗大王批答。称以百世不惑。欲以证其初无可死之义者。十也。夫孔子当时。想只舍其驺从。除其威仪。使衣服凡百与凡人等。欲不令人知孔子也。美村则既为珍原君之奴。未知牵马与否。而美村疏亦谓敌兵与见者。孰不知珍原君之奴云。若只在后而已。又岂能必知其为奴乎。然则其比之于孔子之微服。可谓大僭矣。自古欲死者。本无必欲见父母而后死之义。况美村此时。母夫人亦入江都。何必归见八松公而死乎。若必欲死而倖免。则谓之天亦可。而此则故为欲生而为珍原君之奴矣。其以不死。归之于天者。何也。权,金两公。设或邂逅致死。今固不当以为在南门之故。况其以死自誓者明白。其何忍为此言耶。且既隶在南
之义者。三也。以美村一生引咎为自道之辞。而为 孝宗言之。欲效无忘在莒之义者。四也。以美村终身不出为。非以江都事也。实为量时量己量人者。五也。谓美村平生。不以微意示人。人无知者。同春,松谷所白。亦未能尽者。六也。以美村死罪之称谓。以违命为大罪。而引丁酉戊戌两疏而证之者。七也。以訾病美村者。谓同于訾病栗谷者。八也。谓栗谷犹真有入山之失。以江都事。为胜于入山者。九也。引 孝宗大王批答。称以百世不惑。欲以证其初无可死之义者。十也。夫孔子当时。想只舍其驺从。除其威仪。使衣服凡百与凡人等。欲不令人知孔子也。美村则既为珍原君之奴。未知牵马与否。而美村疏亦谓敌兵与见者。孰不知珍原君之奴云。若只在后而已。又岂能必知其为奴乎。然则其比之于孔子之微服。可谓大僭矣。自古欲死者。本无必欲见父母而后死之义。况美村此时。母夫人亦入江都。何必归见八松公而死乎。若必欲死而倖免。则谓之天亦可。而此则故为欲生而为珍原君之奴矣。其以不死。归之于天者。何也。权,金两公。设或邂逅致死。今固不当以为在南门之故。况其以死自誓者明白。其何忍为此言耶。且既隶在南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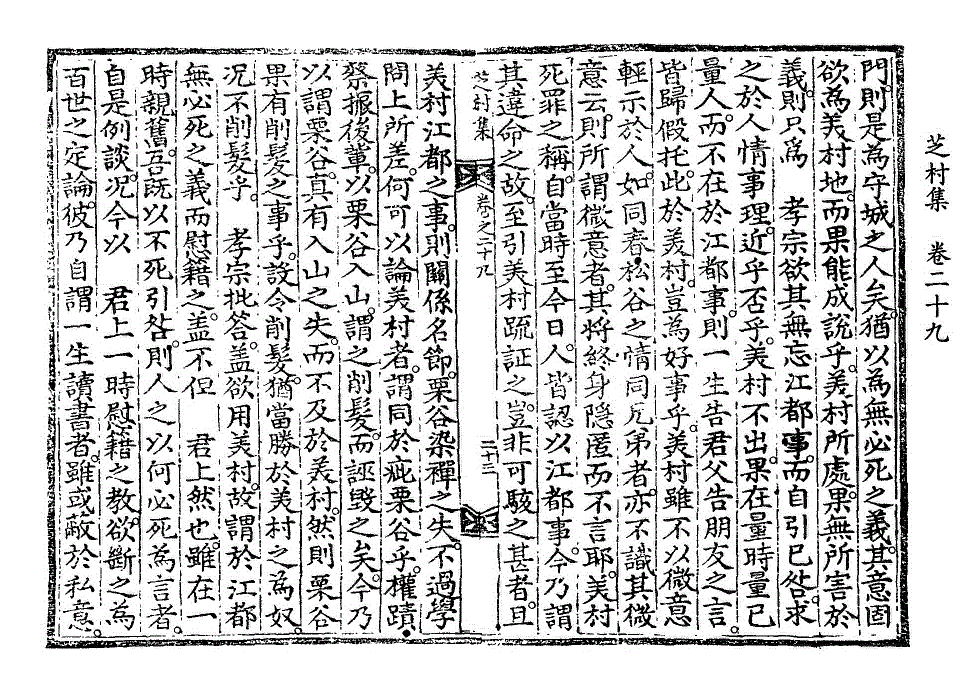 门。则是为守城之人矣。犹以为无必死之义。其意固欲为美村地。而果能成说乎。美村所处。果无所害于义。则只为 孝宗欲其无忘江都事。而自引己咎。求之于人情事理。近乎否乎。美村不出。果在量时量己量人。而不在于江都事。则一生告君父告朋友之言。皆归假托。此于美村。岂为好事乎。美村虽不以微意轻示于人。如同春,松谷之情同兄弟者。亦不识其微意云。则所谓微意者。其将终身隐匿而不言耶。美村死罪之称。自当时至今日。人皆认以江都事。今乃谓其违命之故。至引美村疏证之。岂非可骇之甚者。且美村江都之事。则关系名节。栗谷染禅之失。不过学问上所差。何可以论美村者。谓同于疵栗谷乎。权迹,蔡振后辈。以栗谷入山。谓之削发。而诬毁之矣。今乃以谓栗谷。真有入山之失。而不及于美村。然则栗谷果有削发之事乎。设令削发。犹当胜于美村之为奴。况不削发乎。 孝宗批答。盖欲用美村。故谓于江都无必死之义而慰籍之。盖不但 君上然也。虽在一时亲旧。吾既以不死引咎。则人之以何必死为言者。自是例谈。况今以 君上一时慰籍之教。欲断之为百世之定论。彼乃自谓一生读书者。虽或蔽于私意。
门。则是为守城之人矣。犹以为无必死之义。其意固欲为美村地。而果能成说乎。美村所处。果无所害于义。则只为 孝宗欲其无忘江都事。而自引己咎。求之于人情事理。近乎否乎。美村不出。果在量时量己量人。而不在于江都事。则一生告君父告朋友之言。皆归假托。此于美村。岂为好事乎。美村虽不以微意轻示于人。如同春,松谷之情同兄弟者。亦不识其微意云。则所谓微意者。其将终身隐匿而不言耶。美村死罪之称。自当时至今日。人皆认以江都事。今乃谓其违命之故。至引美村疏证之。岂非可骇之甚者。且美村江都之事。则关系名节。栗谷染禅之失。不过学问上所差。何可以论美村者。谓同于疵栗谷乎。权迹,蔡振后辈。以栗谷入山。谓之削发。而诬毁之矣。今乃以谓栗谷。真有入山之失。而不及于美村。然则栗谷果有削发之事乎。设令削发。犹当胜于美村之为奴。况不削发乎。 孝宗批答。盖欲用美村。故谓于江都无必死之义而慰籍之。盖不但 君上然也。虽在一时亲旧。吾既以不死引咎。则人之以何必死为言者。自是例谈。况今以 君上一时慰籍之教。欲断之为百世之定论。彼乃自谓一生读书者。虽或蔽于私意。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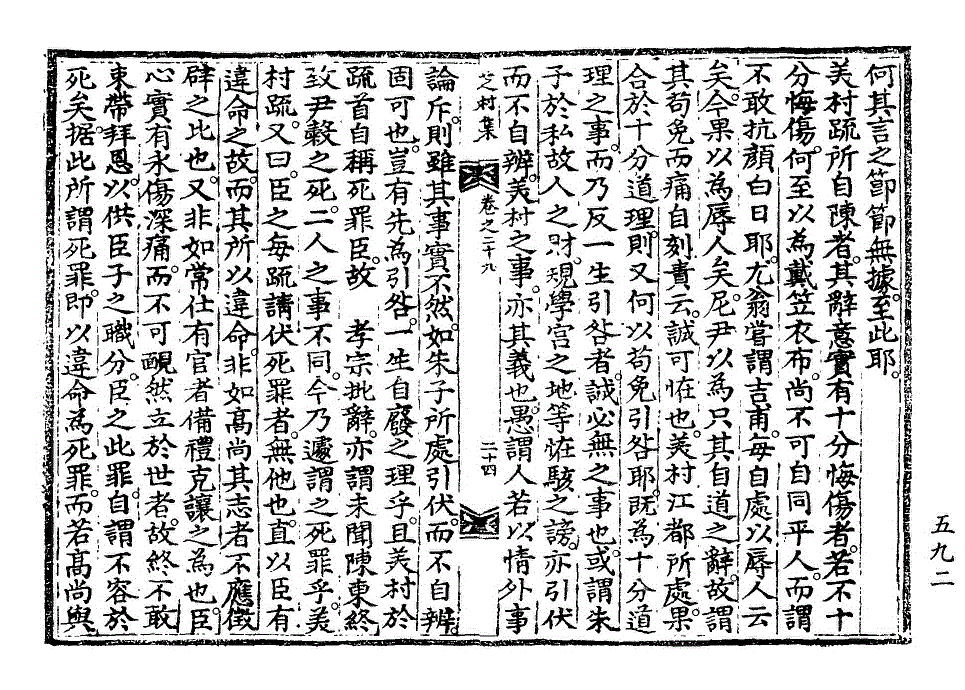 何其言之节节无据。至此耶。
何其言之节节无据。至此耶。美村疏所自陈者。其辞意实有十分悔伤者。若不十分悔伤。何至以为戴笠衣布。尚不可自同平人。而谓不敢抗颜白日耶。尤翁尝谓吉甫。每自处以辱人云矣。今果以为辱人矣。尼尹以为只其自道之辞。故谓其苟免而痛自刻责云。诚可怪也。美村江都所处。果合于十分道理。则又何以苟免引咎耶。既为十分道理之事。而乃反一生引咎者。诚必无之事也。或谓朱子于私故人之财。规学宫之地等怪骇之谤。亦引伏而不自辨。美村之事。亦其义也。愚谓人若以情外事论斥。则虽其事实不然。如朱子所处引伏。而不自辨。固可也。岂有先为引咎。一生自废之理乎。且美村于疏首自称死罪臣。故 孝宗批辞。亦谓未闻陈东终致尹谷之死。二人之事不同。今乃遽谓之死罪乎。美村疏。又曰。臣之每疏请伏死罪者。无他也。直以臣有违命之故。而其所以违命。非如高尚其志者不应徵辟之比也。又非如常仕有官者备礼克让之为也。臣心实有永伤深痛。而不可腼然立于世者。故终不敢束带拜恩。以供臣子之职分。臣之此罪。自谓不容于死矣。据此所谓死罪。即以违命为死罪。而若高尚与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第 5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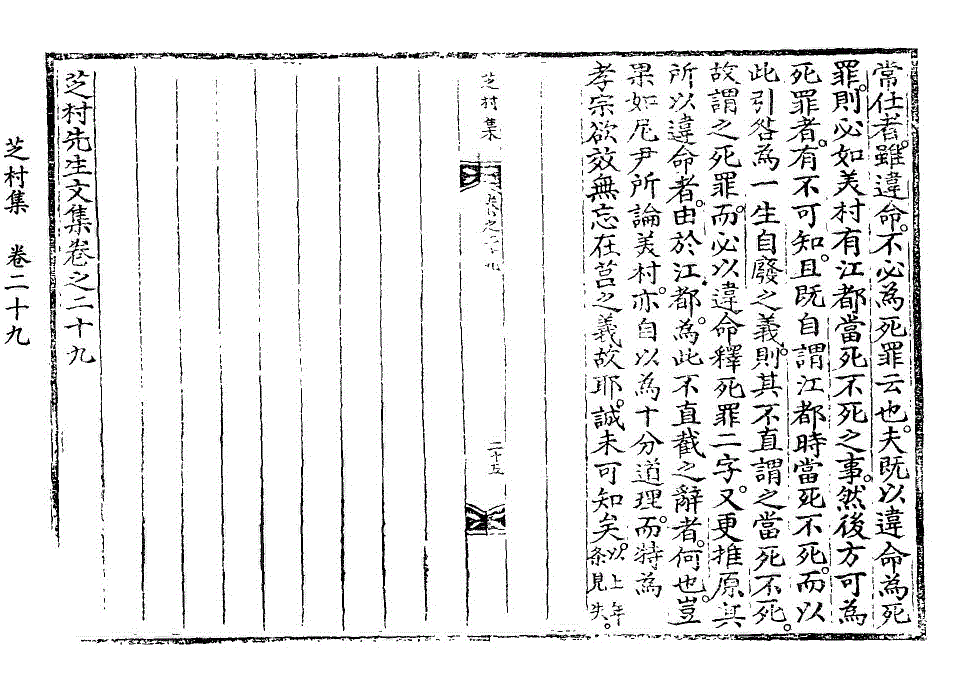 常仕者。虽违命。不必为死罪云也。夫既以违命为死罪。则必如美村有江都当死不死之事。然后方可为死罪者。有不可知。且既自谓江都时当死不死。而以此引咎为一生自废之义。则其不直谓之当死不死。故谓之死罪。而必以违命释死罪二字。又更推原其所以违命者。由于江都。为此不直截之辞者。何也。岂果如尼尹所论美村。亦自以为十分道理。而特为 孝宗欲效无忘在莒之义故耶。诚未可知矣。(以上年条见失。)
常仕者。虽违命。不必为死罪云也。夫既以违命为死罪。则必如美村有江都当死不死之事。然后方可为死罪者。有不可知。且既自谓江都时当死不死。而以此引咎为一生自废之义。则其不直谓之当死不死。故谓之死罪。而必以违命释死罪二字。又更推原其所以违命者。由于江都。为此不直截之辞者。何也。岂果如尼尹所论美村。亦自以为十分道理。而特为 孝宗欲效无忘在莒之义故耶。诚未可知矣。(以上年条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