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x 页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杂记
杂记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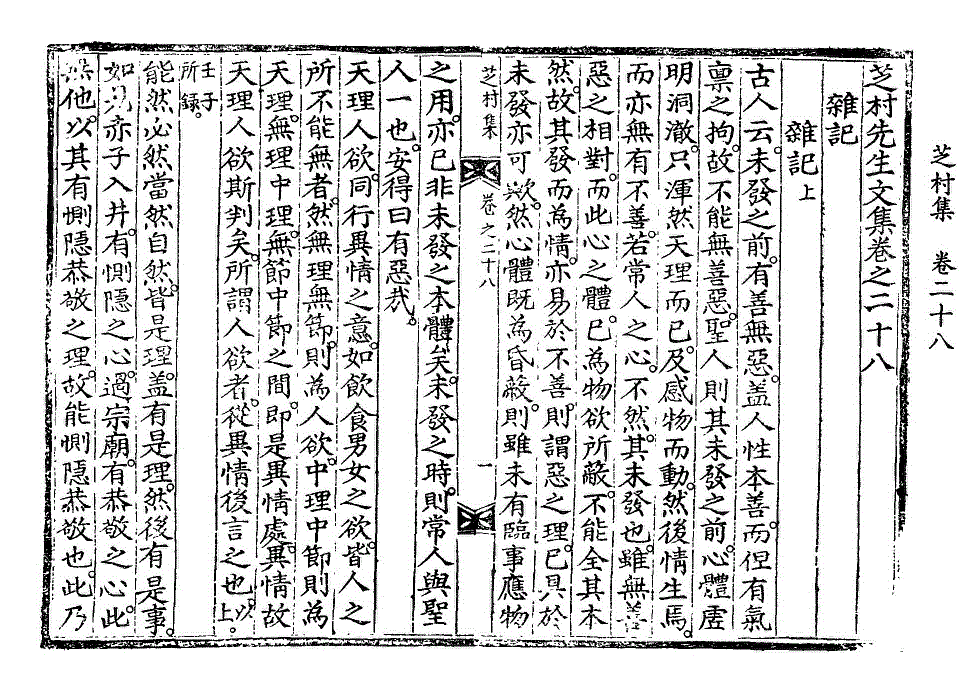 杂记(上)
杂记(上)古人云。未发之前。有善无恶。盖人性本善。而但有气禀之拘。故不能无善恶。圣人则其未发之前。心体虚明洞澈。只浑然天理而已。及感物而动。然后情生焉。而亦无有不善。若常人之心。不然。其未发也。虽无善恶之相对。而此心之体。已为物欲所蔽。不能全其本然。故其发而为情。亦易于不善。则谓恶之理。已具于未发亦可欤。然心体既为昏蔽。则虽未有临事应物之用。亦已非未发之本体矣。未发之时。则常人与圣人一也。安得曰有恶哉。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意。如饮食男女之欲。皆人之所不能无者。然无理无节。则为人欲。中理中节则为天理。无理中理。无节中节之间。即是异情处。异情故天理人欲斯判矣。所谓人欲者。从异情后言之也。(以上。壬子所录。)
能然必然当然自然。皆是理。盖有是理。然后有是事。如见赤子入井。有恻隐之心。过宗庙。有恭敬之心。此无他。以其有恻隐恭敬之理。故能恻隐恭敬也。此乃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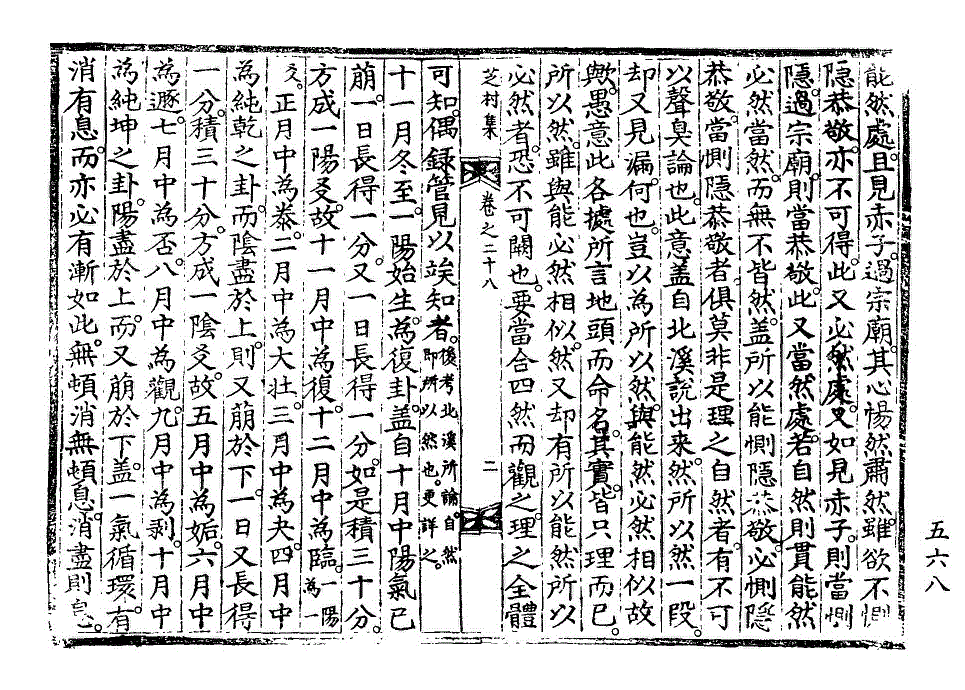 能然处。且见赤子。过宗庙。其心惕然肃然。虽欲不恻隐恭敬。亦不可得。此又必然处。又如见赤子。则当恻隐。过宗庙。则当恭敬。此又当然处。若自然则贯能然必然当然。而无不皆然。盖所以能恻隐恭敬。必恻隐恭敬。当恻隐恭敬者。俱莫非是理之自然者。有不可以声臭论也。此意盖自北溪说出来。然所以然一段。却又见漏。何也。岂以为所以然。与能然必然相似故欤。愚意此各据所言地头而命名。其实。皆只理而已。所以然。虽与能必然相似。然又却有所以能然所以必然者。恐不可阙也。要当合四然而观之。理之全体可知。偶录管见以俟知者。(后考北溪所论。自然即所以然也。更详之。)
能然处。且见赤子。过宗庙。其心惕然肃然。虽欲不恻隐恭敬。亦不可得。此又必然处。又如见赤子。则当恻隐。过宗庙。则当恭敬。此又当然处。若自然则贯能然必然当然。而无不皆然。盖所以能恻隐恭敬。必恻隐恭敬。当恻隐恭敬者。俱莫非是理之自然者。有不可以声臭论也。此意盖自北溪说出来。然所以然一段。却又见漏。何也。岂以为所以然。与能然必然相似故欤。愚意此各据所言地头而命名。其实。皆只理而已。所以然。虽与能必然相似。然又却有所以能然所以必然者。恐不可阙也。要当合四然而观之。理之全体可知。偶录管见以俟知者。(后考北溪所论。自然即所以然也。更详之。)十一月冬至。一阳始生。为复卦。盖自十月中阳气已萌。一日长得一分。又一日长得一分。如是积三十分。方成一阳爻。故十一月中为复。十二月中为临。(一阳为一爻。)正月中为泰。二月中为大壮。三月中为夬。四月中为纯乾之卦。而阴尽于上。则又萌于下。一日又长得一分。积三十分。方成一阴爻。故五月中为姤。六月中为遁。七月中为否。八月中为观。九月中为剥。十月中为纯坤之卦。阳尽于上。而又萌于下。盖一气循环。有消有息。而亦必有渐如此。无顿消无顿息。消尽则息。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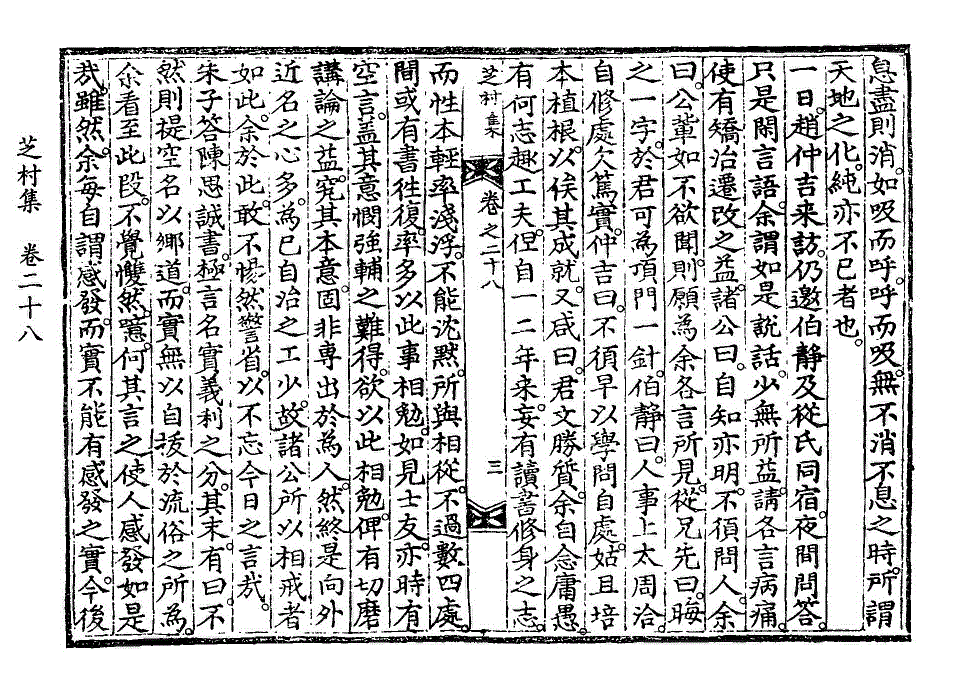 息尽则消。如吸而呼。呼而吸。无不消不息之时。所谓天地之化。纯亦不已者也。
息尽则消。如吸而呼。呼而吸。无不消不息之时。所谓天地之化。纯亦不已者也。一日。赵仲吉来访。仍邀伯静及从氏同宿。夜间问答。只是闲言语。余谓如是说话。少无所益。请各言病痛。使有矫治迁改之益。诸公曰。自知亦明。不须问人。余曰。公辈如不欲闻。则愿为余各言所见。从兄先曰。晦之一字。于君可为顶门一针。伯静曰。人事上太周洽。自修处欠笃实。仲吉曰。不须早以学问自处。姑且培本植根。以俟其成就。又咸曰。君文胜质。余自念庸愚。有何志趣工夫。但自一二年来。妄有读书修身之志。而性本轻率浅浮。不能沈默。所与相从。不过数四处。间或有书往复。率多以此事相勉。如见士友。亦时有空言。盖其意悯强辅之难得。欲以此相勉。俾有切磨讲论之益。究其本意。固非专出于为人。然终是向外近名之心多。为己自治之工少。故诸公所以相戒者如此。余于此。敢不惕然警省。以不忘今日之言哉。
朱子答陈思诚书。极言名实义利之分。其末。有曰。不然则提空名以乡道。而实无以自拔于流俗之所为。余看至此段。不觉𢥠然。噫。何其言之使人感发如是哉。虽然。余每自谓感发。而实不能有感发之实。今后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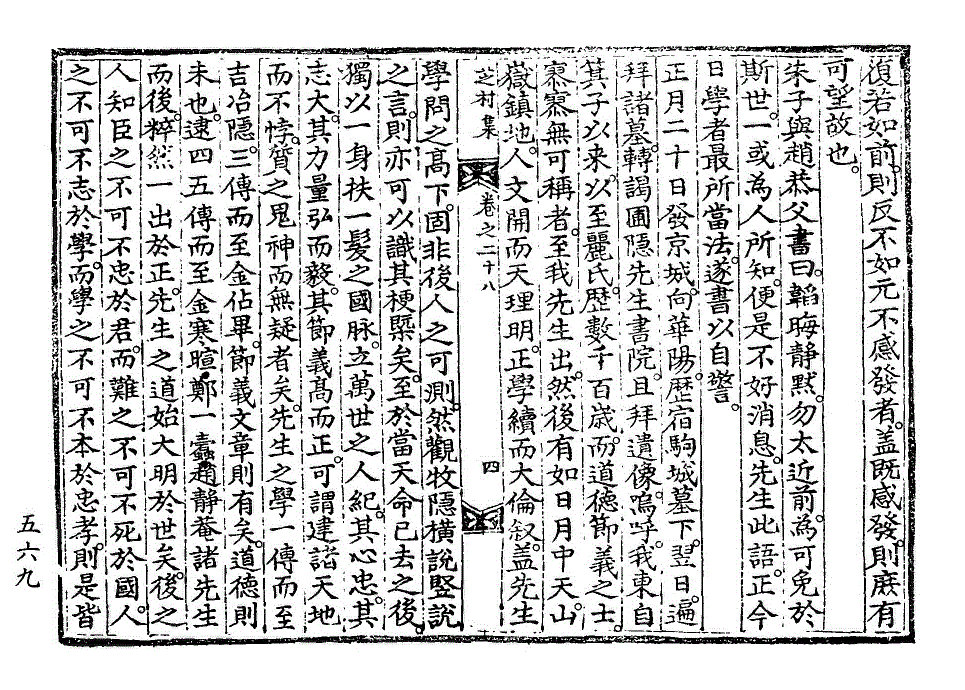 复若如前。则反不如元不感发者。盖既感发。则庶有可望故也。
复若如前。则反不如元不感发者。盖既感发。则庶有可望故也。朱子与赵恭父书曰。韬晦静默。勿太近前。为可免于斯世。一或为人所知。便是不好消息。先生此语。正今日学者最所当法。遂书以自警。
正月二十日发京城。向华阳。历宿驹城墓下。翌日。遍拜诸墓。转谒圃隐先生书院。且拜遗像。呜呼。我东自箕子以来。以至丽氏。历数千百岁。而道德节义之士。寥寥无可称者。至我先生出。然后有如日月中天。山岳镇地。人文开而天理明。正学续而大伦叙。盖先生学问之高下。固非后人之可测。然观牧隐横说竖说之言。则亦可以识其梗槩矣。至于当天命已去之后。独以一身扶一发之国脉。立万世之人纪。其心忠。其志大。其力量弘而毅。其节义高而正。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之鬼神而无疑者矣。先生之学一传而至吉冶隐。三传而至金佔毕。节义文章则有矣。道德则未也。逮四五传而至金寒暄,郑一蠹,赵静庵诸先生而后。粹然一出于正。先生之道始大明于世矣。后之人知臣之不可不忠于君。而难之不可不死于国。人之不可不志于学。而学之不可不本于忠孝。则是皆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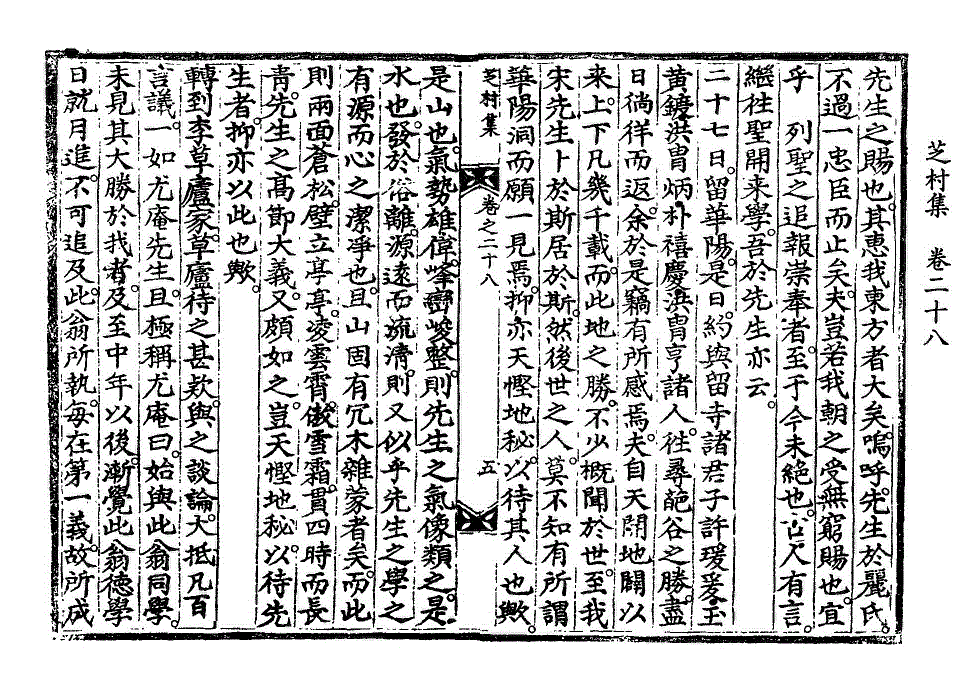 先生之赐也。其惠我东方者大矣。呜呼。先生于丽氏。不过一忠臣而止矣。夫岂若我朝之受无穷赐也。宜乎 列圣之追报崇奉者。至于今未绝也。古人有言。继往圣开来学。吾于先生亦云。
先生之赐也。其惠我东方者大矣。呜呼。先生于丽氏。不过一忠臣而止矣。夫岂若我朝之受无穷赐也。宜乎 列圣之追报崇奉者。至于今未绝也。古人有言。继往圣开来学。吾于先生亦云。二十七日。留华阳。是日。约与留寺诸君子许瑗爰,玉黄镀,洪胄炳,朴禧庆,洪胄亨诸人。往寻葩谷之胜。尽日徜徉而返。余于是窃有所感焉。夫自天开地辟以来。上下凡几千载。而此地之胜。不少概闻于世。至我宋先生卜于斯居于斯。然后世之人。莫不知有所谓华阳洞而愿一见焉。抑亦天悭地秘。以待其人也欤。是山也。气势雄伟。峰峦峻整。则先生之气像类之。是水也。发于俗离。源远而流清。则又似乎先生之学之有源而心之洁净也。且山固有冗木杂蒙者矣。而此则两面苍松。壁立亭亭。凌云霄。傲雪霜。贯四时而长青。先生之高节大义。又颇如之。岂天悭地秘。以待先生者。抑亦以此也欤。
转到李草庐家。草庐待之甚款。与之谈论。大抵凡百言议。一如尤庵先生。且极称尤庵曰。始与此翁同学。未见其大胜于我者。及至中年以后。渐觉此翁德学日就月进。不可追及。此翁所执。每在第一义。故所成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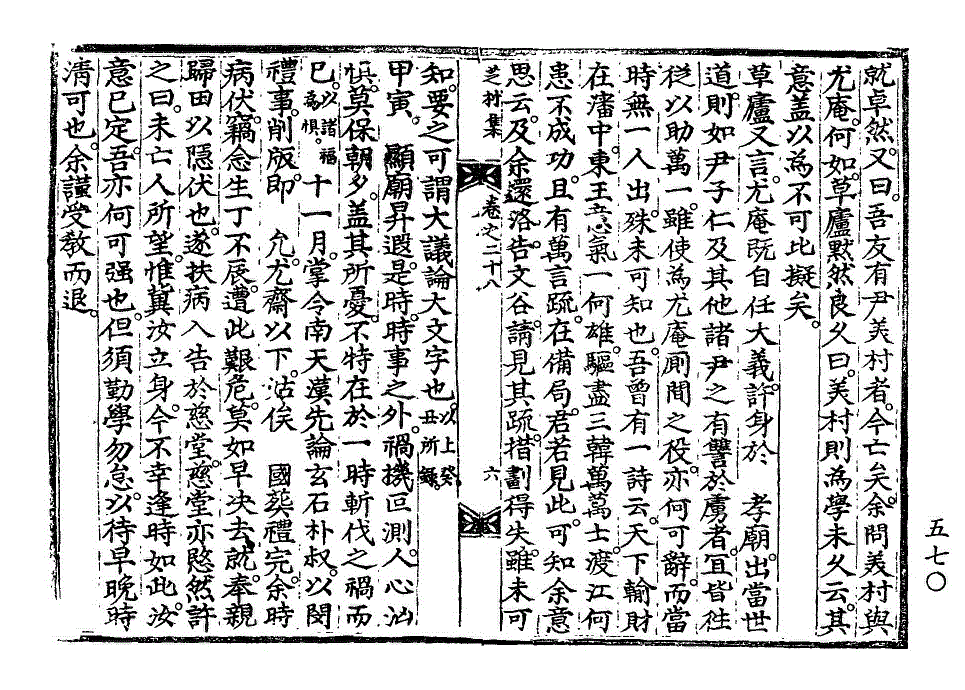 就卓然。又曰。吾友有尹美村者。今亡矣。余问美村与尤庵。何如。草庐默然良久曰。美村则为学未久云。其意盖以为不可比拟矣。
就卓然。又曰。吾友有尹美村者。今亡矣。余问美村与尤庵。何如。草庐默然良久曰。美村则为学未久云。其意盖以为不可比拟矣。草庐又言。尤庵既自任大义。许身于 孝庙。出当世道。则如尹子仁及其他诸尹之有雠于虏者。宜皆往从以助万一。虽使为尤庵厕间之役。亦何可辞。而当时无一人出。殊未可知也。吾曾有一诗云。天下输财在沈中。东王意气一何雄。驱尽三韩万万士。渡江何患不成功。且有万言疏。在备局。君若见此。可知余意思云。及余还洛。告文谷。请见其疏。措划得失。虽未可知。要之可谓大议论大文字也。(以上癸丑所录。)
甲寅。 显庙升遐。是时。时事之外。祸机叵测。人心汹惧。莫保朝夕。盖其所忧。不特在于一时斩伐之祸而已。(以诸福为惧。)十一月。掌令南天汉先论玄石朴叔。以闵礼事。削版。即 允。尤斋以下。姑俟 国葬礼完。余时病伏。窃念生丁不辰。遭此艰危。莫如早决去就。奉亲归田以隐伏也。遂扶病入告于慈堂。慈堂亦悯然许之曰。未亡人所望。惟冀汝立身。今不幸逢时如此。汝意已定。吾亦何可强也。但须勤学勿怠。以待早晚时清可也。余谨受教而退。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1H 页
 余自十六七岁。窃尝有志于从善。及后出入师友之间。亦且有观感之益。身心书册工夫。皆粗专一。顾立志未坚固。且自甲寅祸作之后。实有逃世出尘之意。家贫亲病。未易如意。以未即入山为大烦恼。最晚始结茅芝洞。至冬乃卷归焉。白地栖泊。无以聊生。留心学农。或至身亲莅之。如是荏苒。自然二寒暑矣。其间绝不得着工。放废几不能收拾。今日偶阅朱子语类。惕然有感奋之意。不知今后复如何否。玆书以识之。六月二十一日夜。书。
余自十六七岁。窃尝有志于从善。及后出入师友之间。亦且有观感之益。身心书册工夫。皆粗专一。顾立志未坚固。且自甲寅祸作之后。实有逃世出尘之意。家贫亲病。未易如意。以未即入山为大烦恼。最晚始结茅芝洞。至冬乃卷归焉。白地栖泊。无以聊生。留心学农。或至身亲莅之。如是荏苒。自然二寒暑矣。其间绝不得着工。放废几不能收拾。今日偶阅朱子语类。惕然有感奋之意。不知今后复如何否。玆书以识之。六月二十一日夜。书。余性本来躁浮。中间颇有意矫治。少有一分之益。而近因凡百放倒。遇事辄发。不能持重宽和。近日朝夕拜聘翁。日日终夕。虽遇可怒事。未尝见其一施骂詈。以厉声色。盖其资禀宽夷。心地平易。实非浅陋所可及也。玆书于此。以为思齐之资云。
沈龙卿。天资恬静寡言。亦且留意学问。少从玄石游。后又受学于尤斋先生。然气质欠于明彻。见处多含含胡胡。亦无振发奋厉之意。要之尽佳士也。
尤翁祸作后。龙卿称病不仕。有归田读书之意。余谓此固善矣。但君既出入侍从。若能上章。言罪人门徒。不可立朝之意。则出处似明白矣。龙卿不从。余问君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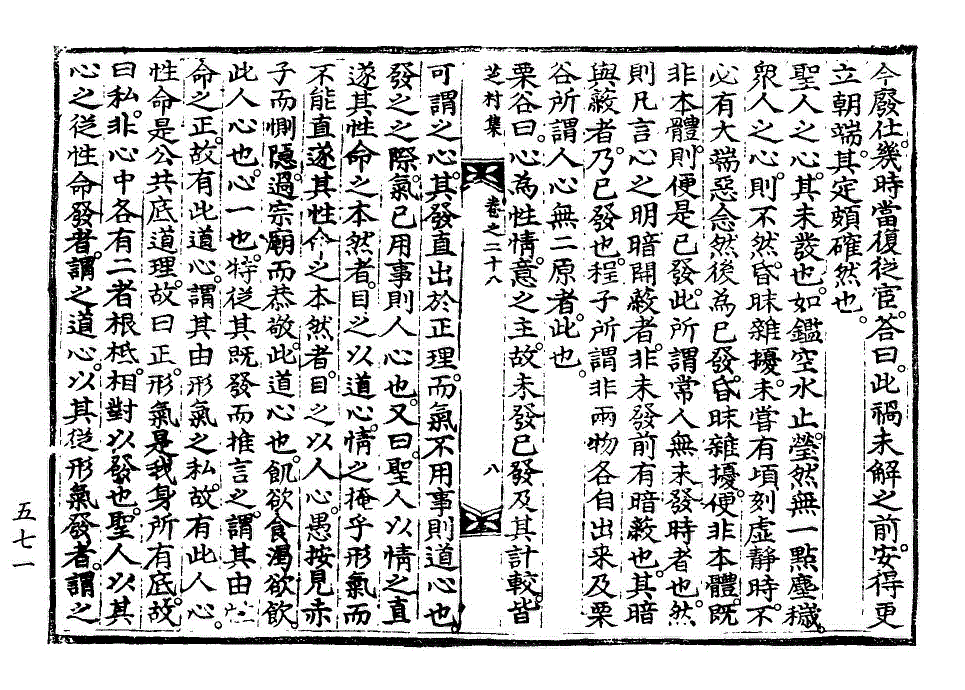 今废仕。几时当复从宦。答曰。此祸未解之前。安得更立朝端。其定颇确然也。
今废仕。几时当复从宦。答曰。此祸未解之前。安得更立朝端。其定颇确然也。圣人之心。其未发也。如鉴空水止。莹然无一点尘秽。众人之心。则不然。昏昧杂扰。未尝有顷刻虚静时。不必有大端恶念然后为已发。昏昧杂扰。便非本体。既非本体。则便是已发。此所谓常人无未发时者也。然则凡言心之明暗开蔽者。非未发前有暗蔽也。其暗与蔽者。乃已发也。程子所谓非两物各自出来及栗谷所谓人心无二原者。此也。
栗谷曰。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又曰。圣人以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愚按见赤子而恻隐。过宗庙而恭敬。此道心也。饥欲食渴欲饮。此人心也。心一也。特从其既发而推言之。谓其由性命之正。故有此道心。谓其由形气之私。故有此人心。性命是公共底道理。故曰正。形气是我身所有底。故曰私。非心中各有二者根柢。相对以发也。圣人以其心之从性命发者。谓之道心。以其从形气发者。谓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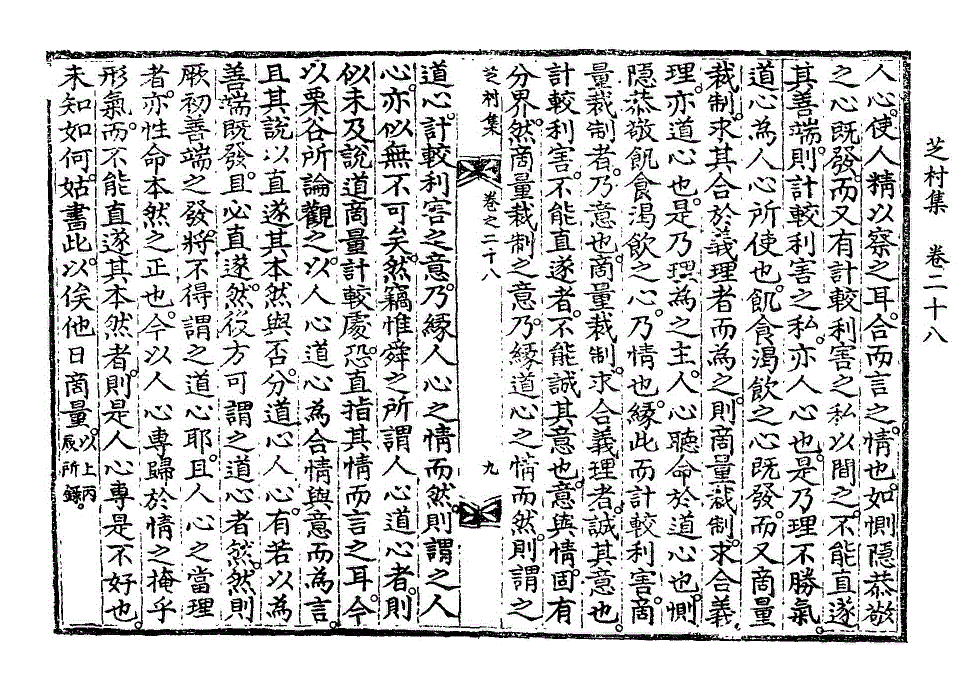 人心。使人精以察之耳。合而言之。情也。如恻隐恭敬之心既发。而又有计较利害之私以间之。不能直遂其善端。则计较利害之私。亦人心也。是乃理不胜气。道心为人心所使也。饥食渴饮之心既发。而又商量裁制。求其合于义理者而为之。则商量裁制。求合义理。亦道心也。是乃理为之主。人心听命于道心也。恻隐恭敬饥食渴饮之心。乃情也。缘此而计较利害。商量裁制者。乃意也。商量裁制。求合义理者。诚其意也。计较利害。不能直遂者。不能诚其意也。意与情。固有分界。然商量裁制之意。乃缘道心之情而然。则谓之道心。计较利害之意。乃缘人心之情而然。则谓之人心。亦似无不可矣。然窃惟舜之所谓人心道心者。则似未及说道商量计较处。恐直指其情而言之耳。今以栗谷所论观之。以人心道心为合情与意而为言。且其说以直遂其本然与否。分道心人心。有若以为善端既发。且必直遂。然后方可谓之道心者然。然则厥初善端之发。将不得谓之道心耶。且人心之当理者。亦性命本然之正也。今以人心专归于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本然者。则是人心专是不好也。未知如何。姑书此。以俟他日商量。(以上丙辰所录。)
人心。使人精以察之耳。合而言之。情也。如恻隐恭敬之心既发。而又有计较利害之私以间之。不能直遂其善端。则计较利害之私。亦人心也。是乃理不胜气。道心为人心所使也。饥食渴饮之心既发。而又商量裁制。求其合于义理者而为之。则商量裁制。求合义理。亦道心也。是乃理为之主。人心听命于道心也。恻隐恭敬饥食渴饮之心。乃情也。缘此而计较利害。商量裁制者。乃意也。商量裁制。求合义理者。诚其意也。计较利害。不能直遂者。不能诚其意也。意与情。固有分界。然商量裁制之意。乃缘道心之情而然。则谓之道心。计较利害之意。乃缘人心之情而然。则谓之人心。亦似无不可矣。然窃惟舜之所谓人心道心者。则似未及说道商量计较处。恐直指其情而言之耳。今以栗谷所论观之。以人心道心为合情与意而为言。且其说以直遂其本然与否。分道心人心。有若以为善端既发。且必直遂。然后方可谓之道心者然。然则厥初善端之发。将不得谓之道心耶。且人心之当理者。亦性命本然之正也。今以人心专归于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本然者。则是人心专是不好也。未知如何。姑书此。以俟他日商量。(以上丙辰所录。)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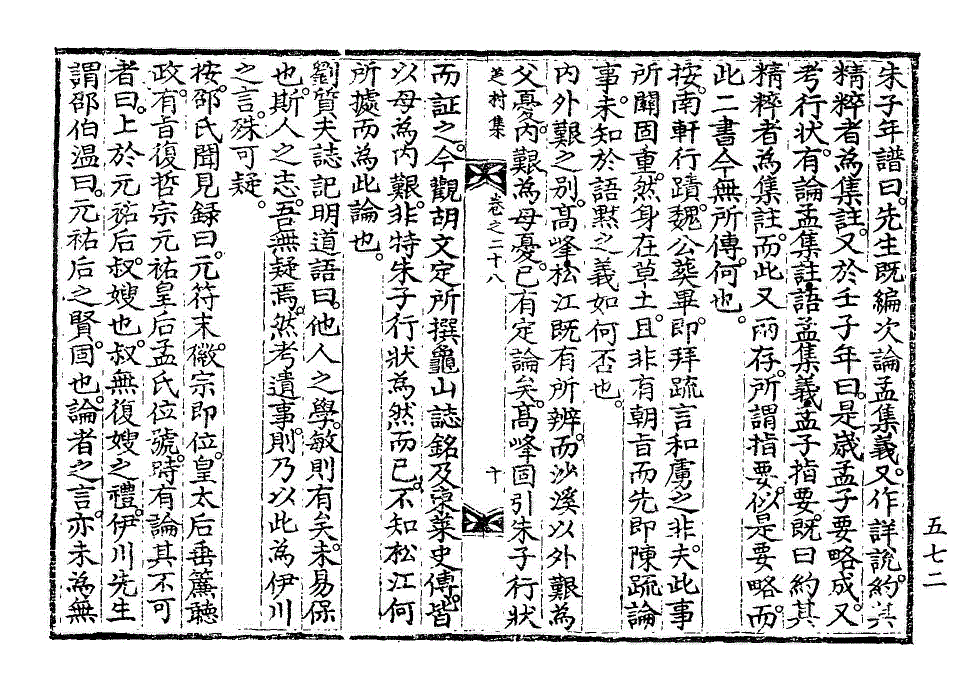 朱子年谱曰。先生既编次论孟集义。又作详说。约其精粹者为集注。又于壬子年曰。是岁孟子要略成。又考行状。有论孟集注,语孟集义,孟子指要。既曰约其精粹者为集注。而此又两存。所谓指要。似是要略。而此二书今无所传。何也。
朱子年谱曰。先生既编次论孟集义。又作详说。约其精粹者为集注。又于壬子年曰。是岁孟子要略成。又考行状。有论孟集注,语孟集义,孟子指要。既曰约其精粹者为集注。而此又两存。所谓指要。似是要略。而此二书今无所传。何也。按。南轩行迹。魏公葬毕。即拜疏言和虏之非。夫此事所关固重。然身在草土。且非有朝旨而先即陈疏论事。未知于语默之义如何否也。
内外艰之别。高峰,松江既有所辨。而沙溪以外艰为父忧。内艰为母忧。已有定论矣。高峰固引朱子行状而证之。今观胡文定所撰龟山志铭及东莱史传。皆以母为内艰。非特朱子行状为然而已。不知松江何所据而为此论也。
刘质夫志记明道语曰。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无疑焉。然考遗事。则乃以此为伊川之言。殊可疑。
按。邵氏闻见录曰。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有旨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伊川先生谓邵伯温曰。元祐后之贤。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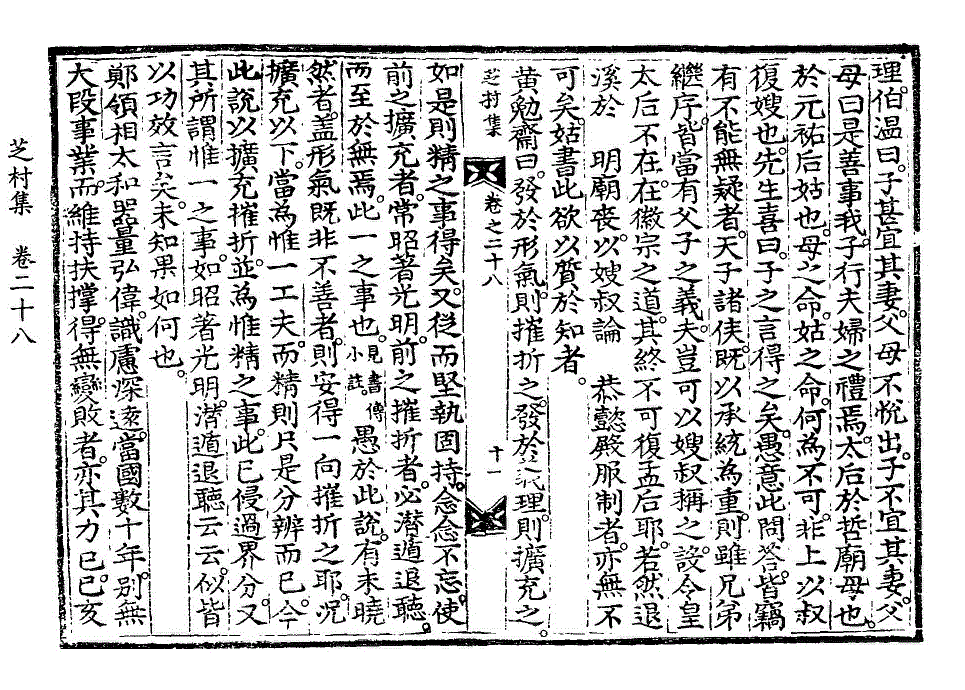 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愚意此问答。皆窃有不能无疑者。天子诸侯。既以承统为重。则虽兄弟继序。皆当有父子之义。夫岂可以嫂叔称之。设令皇太后不在。在徽宗之道。其终不可复孟后耶。若然退溪于 明庙丧。以嫂叔论 恭懿殿服制者。亦无不可矣。姑书此欲以质于知者。
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愚意此问答。皆窃有不能无疑者。天子诸侯。既以承统为重。则虽兄弟继序。皆当有父子之义。夫岂可以嫂叔称之。设令皇太后不在。在徽宗之道。其终不可复孟后耶。若然退溪于 明庙丧。以嫂叔论 恭懿殿服制者。亦无不可矣。姑书此欲以质于知者。黄勉斋曰。发于形气。则摧折之。发于义理。则扩充之。如是则精之事得矣。又从而坚执固持。念念不忘。使前之扩充者。常昭著光明。前之摧折者。必潜遁退听。而至于无焉。此一之事也。(见书传小注。)愚于此说。有未晓然者。盖形气既非不善者。则安得一向摧折之耶。况扩充以下。当为惟一工夫。而精则只是分辨而已。今此说以扩充摧折。并为惟精之事。此已侵过界分。又其所谓惟一之事。如昭著光明。潜遁退听云云。似皆以功效言矣。未知果如何也。
郑领相太和器量弘伟。识虑深远。当国数十年。别无大段事业。而维持扶撑。得无变败者。亦其力已。己亥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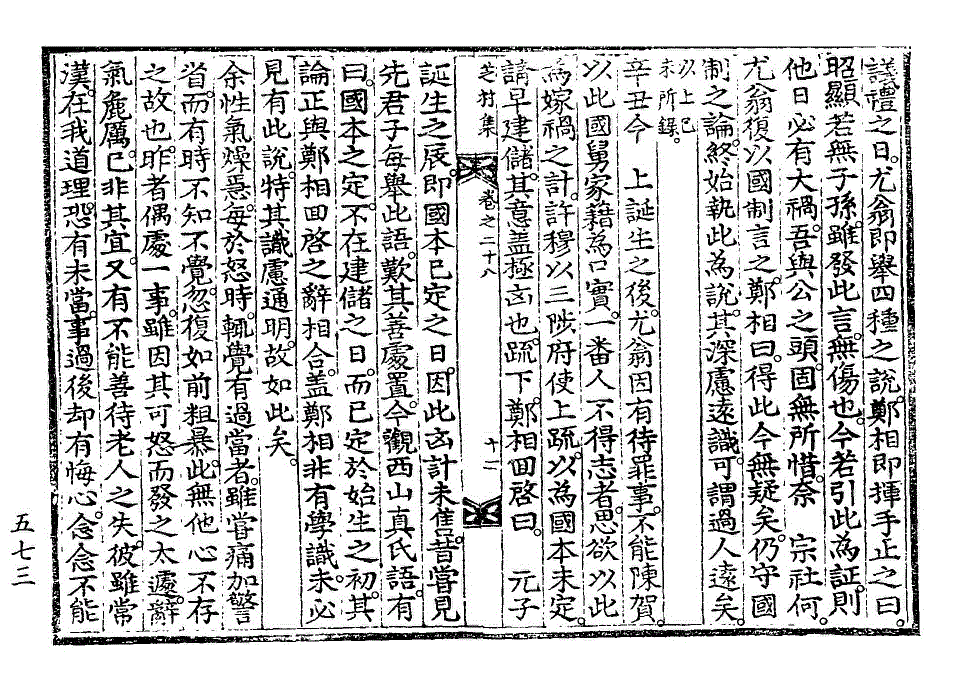 议礼之日。尤翁即举四种之说。郑相即挥手止之曰。昭显若无子孙。虽发此言。无伤也。今若引此为证。则他日必有大祸。吾与公之头。固无所惜。奈 宗社何。尤翁复以国制言之。郑相曰。得此今无疑矣。仍守国制之论。终始执此为说。其深虑远识。可谓过人远矣。(以上己未所录。)
议礼之日。尤翁即举四种之说。郑相即挥手止之曰。昭显若无子孙。虽发此言。无伤也。今若引此为证。则他日必有大祸。吾与公之头。固无所惜。奈 宗社何。尤翁复以国制言之。郑相曰。得此今无疑矣。仍守国制之论。终始执此为说。其深虑远识。可谓过人远矣。(以上己未所录。)辛丑今 上诞生之后。尤翁因有待罪事。不能陈贺。以此国舅家藉为口实。一番人不得志者。思欲以此为嫁祸之计。许穆以三陟府使上疏。以为国本未定。请早建储。其意盖极凶也。疏下。郑相回启曰。 元子诞生之辰。即国本已定之日。因此凶计未售。昔尝见先君子每举此语。叹其善处置。今观西山真氏语。有曰。国本之定。不在建储之日。而已定于始生之初。其论正与郑相回启之辞相合。盖郑相非有学识。未必见有此说。特其识虑通明。故如此矣。
余性气燥急。每于怒时。辄觉有过当者。虽尝痛加警省。而有时不知不觉。忽复如前粗暴。此无他心不存之故也。昨者偶处一事。虽因其可怒而发之太遽。辞气粗厉。已非其宜。又有不能善待老人之失。彼虽常汉。在我道理。恐有未当。事过后却有悔心。念念不能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4H 页
 忘。噫。程子有言。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思过半矣。又曰。不可长留在胸中为悔。此二言者。皆未尝有所得力而然也。可不戒哉。聊书以志之。
忘。噫。程子有言。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思过半矣。又曰。不可长留在胸中为悔。此二言者。皆未尝有所得力而然也。可不戒哉。聊书以志之。余为拜妇翁。往金村。阻雨留一日。偶看栗谷集论民弊处。因问法令条制于妇翁。妇翁为余言之颇详。余又因此略论救弊之策。妇翁或可或不可。且曰。若一委于我而使我担当变通。则虽不得为大事业。岂不可粗有成效云。盖妇翁于政事。最有才识。故自任如此。但念通敏精明。固为长处。而似亦有不能慎重之病。不知事到手头。果如何处之也。
归时。又拜玄石一宿。玄石极论自家去就之义。且曰。古人有身未出而进言者否。其义如何。余对曰。古人事则未可知。但以朱子所谓韦布当言之义推之。身虽未出。进言亦无不可矣。因问若不免一出。今日所当言者。何事为先。玄石曰。外戚诸人。有功国家。不可不善待。而亦当使之畏慎。余曰。义固如此。但以山林处士。一朝出来。而先发善待外戚之论。亦未知如何。玄石曰。固然。却可更容商量。盖是时。玄石连承 召命。观其意。终以承当为难。且未详 上意时势之如何。姑以不出为定。只以假说问答如此。盖今日士类。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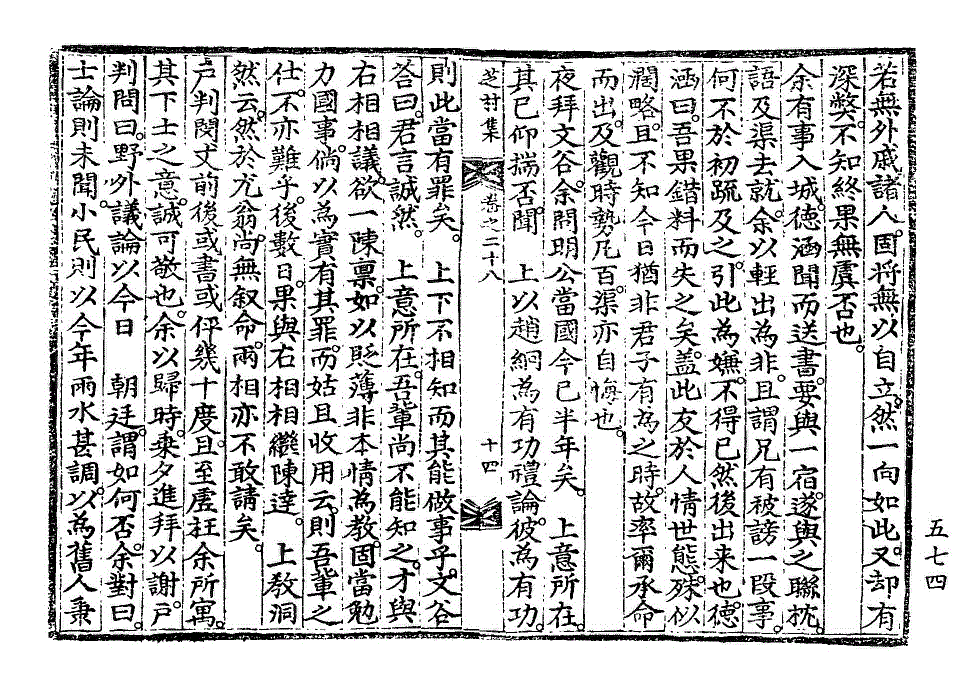 若无外戚诸人。固将无以自立。然一向如此。又却有深弊。不知终果无虞否也。
若无外戚诸人。固将无以自立。然一向如此。又却有深弊。不知终果无虞否也。余有事入城。德涵闻而送书。要与一宿。遂与之联枕。语及渠去就。余以轻出为非。且谓兄有被谤一段事。何不于初疏及之。引此为嫌。不得已然后出来也。德涵曰。吾果错料而失之矣。盖此友于人情世态。殊似阔略。且不知今日犹非君子有为之时。故率尔承命而出。及观时势凡百。渠亦自悔也。
夜拜文谷。余问明公当国今已半年矣。 上意所在。其已仰揣否。闻 上以赵絅为有功礼论。彼为有功。则此当有罪矣。 上下不相知而其能做事乎。文谷答曰。君言诚然。 上意所在。吾辈尚不能知之。才与右相相议。欲一陈禀。如以贬薄非本情为教。固当勉力国事。倘以为实有其罪。而姑且收用云。则吾辈之仕。不亦难乎。后数日。果与右相相继陈达。 上教洞然云。然于尤翁。尚无叙命。两相亦不敢请矣。
户判闵丈前后或书或伻几十度。且至虚枉余所寓。其下士之意。诚可敬也。余以归时。乘夕进拜以谢。户判问曰。野外议论以今日 朝廷。谓如何否。余对曰。士论则未闻。小民则以今年雨水甚调。以为旧人秉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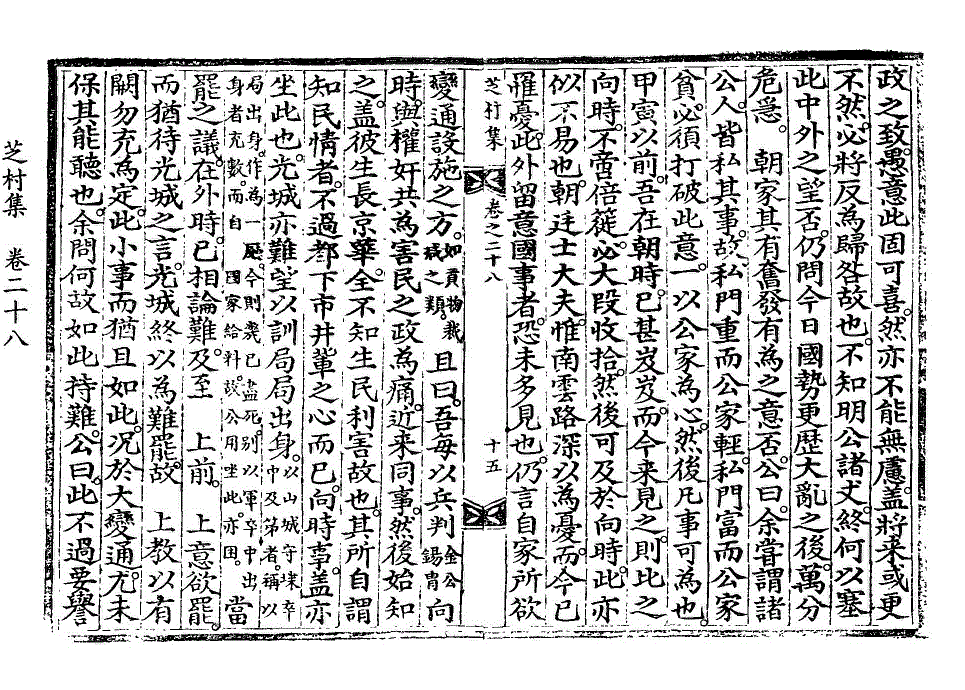 政之致。愚意此固可喜。然亦不能无虑。盖将来或更不然。必将反为归咎故也。不知明公诸丈。终何以塞此中外之望否。仍问今日国势更历大乱之后。万分危急。 朝家其有奋发有为之意否。公曰。余尝谓诸公。人皆私其事。故私门重而公家轻。私门富而公家贫。必须打破此意。一以公家为心。然后凡事可为也。甲寅以前。吾在朝时。已甚岌岌。而今来见之。则比之向时。不啻倍蓰。必大段收拾。然后可及于向时。此亦似不易也。朝廷士大夫。惟南云路深以为忧。而今已罹忧。此外留意国事者。恐未多见也。仍言自家所欲变通设施之方。(如贡物裁减之类。)且曰。吾每以兵判(金公锡胄)向时。与权奸共为害民之政为痛。近来同事。然后始知之。盖彼生长京华。全不知生民利害故也。其所自谓知民情者。不过都下市井辈之心而已。向时事。盖亦坐此也。光城亦难望以训局局出身。(以山城守堞卒中及第者。称以局出身。作为一厅。今则几已尽死。别以军卒中出身者充数。而自 国家给料。故公用坐此。亦困。)当罢之议。在外时。已相论难。及至 上前。 上意欲罢。而犹待光城之言。光城终以为难罢。故 上教以有阙勿充为定。此小事而犹且如此。况于大变通。尤未保其能听也。余问何故如此持难。公曰。此不过要誉
政之致。愚意此固可喜。然亦不能无虑。盖将来或更不然。必将反为归咎故也。不知明公诸丈。终何以塞此中外之望否。仍问今日国势更历大乱之后。万分危急。 朝家其有奋发有为之意否。公曰。余尝谓诸公。人皆私其事。故私门重而公家轻。私门富而公家贫。必须打破此意。一以公家为心。然后凡事可为也。甲寅以前。吾在朝时。已甚岌岌。而今来见之。则比之向时。不啻倍蓰。必大段收拾。然后可及于向时。此亦似不易也。朝廷士大夫。惟南云路深以为忧。而今已罹忧。此外留意国事者。恐未多见也。仍言自家所欲变通设施之方。(如贡物裁减之类。)且曰。吾每以兵判(金公锡胄)向时。与权奸共为害民之政为痛。近来同事。然后始知之。盖彼生长京华。全不知生民利害故也。其所自谓知民情者。不过都下市井辈之心而已。向时事。盖亦坐此也。光城亦难望以训局局出身。(以山城守堞卒中及第者。称以局出身。作为一厅。今则几已尽死。别以军卒中出身者充数。而自 国家给料。故公用坐此。亦困。)当罢之议。在外时。已相论难。及至 上前。 上意欲罢。而犹待光城之言。光城终以为难罢。故 上教以有阙勿充为定。此小事而犹且如此。况于大变通。尤未保其能听也。余问何故如此持难。公曰。此不过要誉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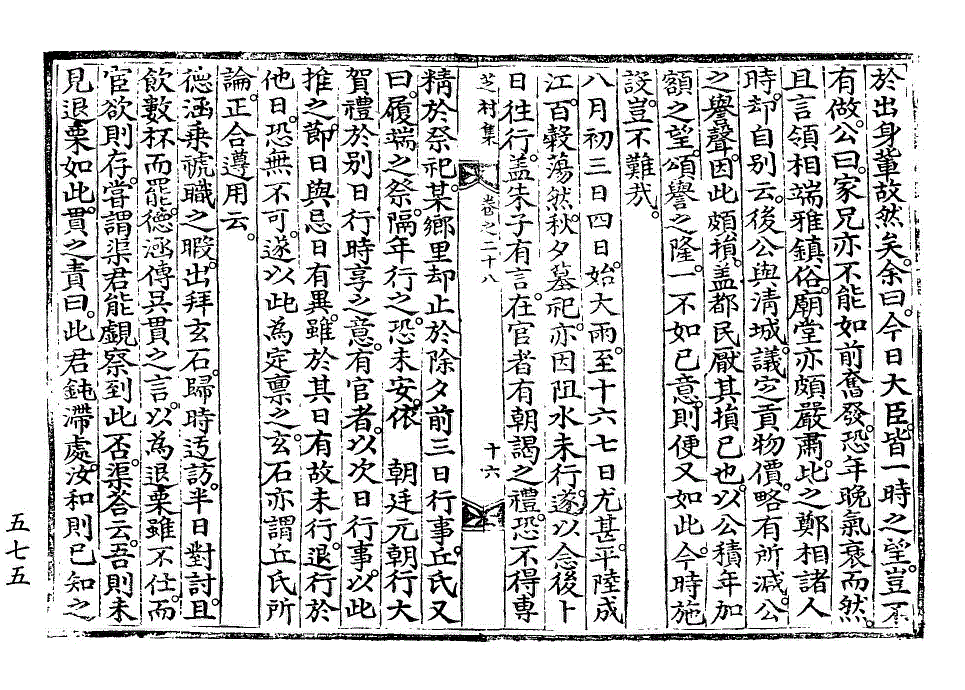 于出身辈故然矣。余曰。今日大臣。皆一时之望。岂不有做。公曰。家兄亦不能如前奋发。恐年晚气衰而然。且言领相端雅镇俗。庙堂亦颇严肃。比之郑相诸人时。却自别云。后公与清城。议定贡物价。略有所减。公之誉声。因此颇损。盖都民厌其损己也。以公积年加额之望。颂誉之隆。一不如己意。则便又如此。今时施设。岂不难哉。
于出身辈故然矣。余曰。今日大臣。皆一时之望。岂不有做。公曰。家兄亦不能如前奋发。恐年晚气衰而然。且言领相端雅镇俗。庙堂亦颇严肃。比之郑相诸人时。却自别云。后公与清城。议定贡物价。略有所减。公之誉声。因此颇损。盖都民厌其损己也。以公积年加额之望。颂誉之隆。一不如己意。则便又如此。今时施设。岂不难哉。八月初三日四日。始大雨。至十六七日尤甚。平陆成江。百谷荡然。秋夕墓祀。亦因阻水未行。遂以念后卜日往行。盖朱子有言。在官者有朝谒之礼。恐不得专精于祭祀。某乡里却止于除夕前三日行事。丘氏又曰。履端之祭。隔年行之。恐未安。依 朝廷元朝行大贺礼于别日行时享之意。有官者。以次日行事。以此推之。节日与忌日有异。虽于其日有故未行。退行于他日。恐无不可。遂以此为定禀之。玄石亦谓丘氏所论。正合遵用云。
德涵乘褫职之暇。出拜玄石。归时迂访。半日对讨。且饮数杯而罢。德涵传吴贯之言。以为退,栗虽不仕。而宦欲则存。尝谓渠君能觑察到此否。渠答云。吾则未见退,栗如此。贯之责曰。此君钝滞处。汝和则已知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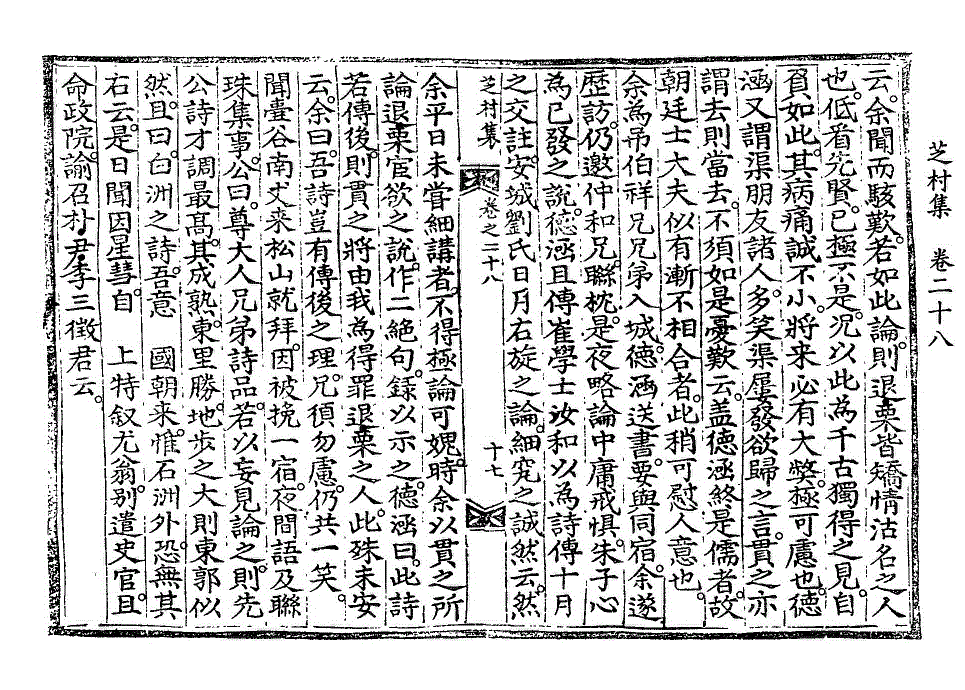 云。余闻而骇叹。若如此论。则退,栗皆矫情沽名之人也。低看先贤。已极不是。况以此为千古独得之见。自负如此。其病痛诚不小。将来必有大弊。极可虑也。德涵又谓渠朋友诸人。多笑渠屡发欲归之言。贯之亦谓去则当去。不须如是忧叹云。盖德涵终是儒者。故朝廷士大夫似有渐不相合者。此稍可慰人意也。
云。余闻而骇叹。若如此论。则退,栗皆矫情沽名之人也。低看先贤。已极不是。况以此为千古独得之见。自负如此。其病痛诚不小。将来必有大弊。极可虑也。德涵又谓渠朋友诸人。多笑渠屡发欲归之言。贯之亦谓去则当去。不须如是忧叹云。盖德涵终是儒者。故朝廷士大夫似有渐不相合者。此稍可慰人意也。余为吊伯祥兄兄弟入城。德涵送书。要与同宿。余遂历访。仍邀仲和兄。联枕。是夜略论中庸戒惧。朱子心为已发之说。德涵且传崔学士汝和以为诗传十月之交注。安城刘氏日月右旋之论。细究之诚然云。然余平日未尝细讲者。不得极论可愧。时余以贯之所论退,栗宦欲之说。作二绝句。录以示之。德涵曰。此诗若传后。则贯之将由我为得罪退,栗之人。此殊未安云。余曰。吾诗岂有传后之理。兄须勿虑。仍共一笑。
闻壶谷南丈来松山就拜。因被挽一宿。夜间语及联珠集事。公曰。尊大人兄弟诗品。若以妄见论之。则先公诗才调最高。其成熟。东里胜。地步之大则东郭似然。且曰。白洲之诗。吾意 国朝来。惟石洲外。恐无其右云。是日闻因星彗。自 上特叙尤翁。别遣史官。且命政院。谕召朴,尹,李三徵君云。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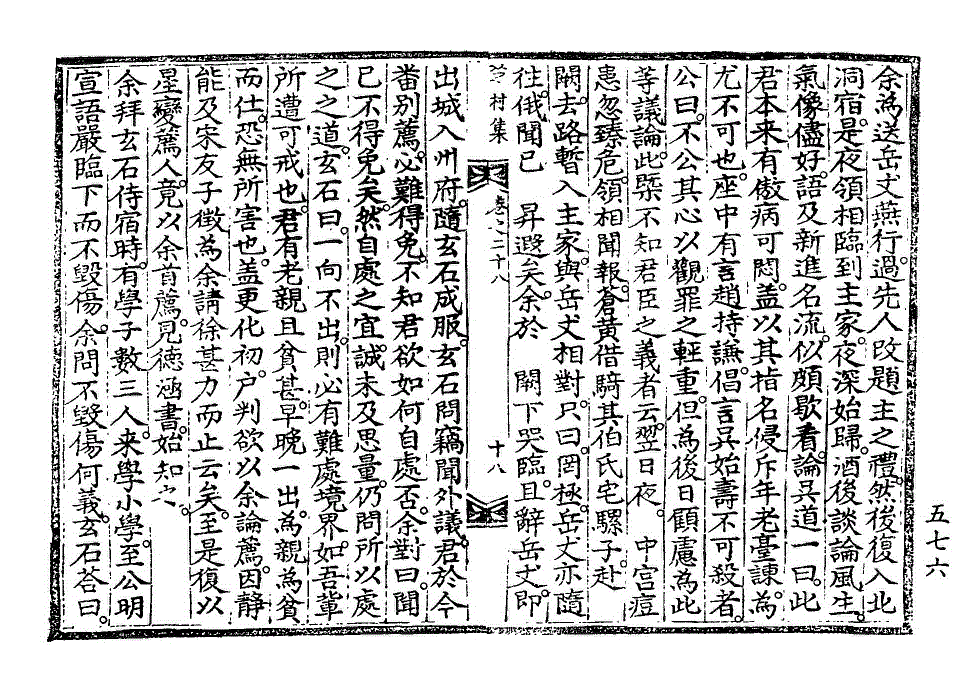 余为送岳丈燕行。过先人改题主之礼。然后复入北洞宿。是夜领相临到主家。夜深始归。酒后谈论风生。气像尽好。语及新进名流。似颇歇看。论吴道一曰。此君本来有傲病可闷。盖以其指名侵斥年老台谏。为尤不可也。座中有言赵持谦。倡言吴始寿不可杀者。公曰。不公其心以观罪之轻重。但为后日顾虑为此等议论。此槩不知君臣之义者云。翌日夜。 中宫痘患忽臻危。领相闻报。苍黄借骑其伯氏宅骡子。赴 阙。去路暂入主家。与岳丈相对。只曰。罔极。岳丈亦随往。俄闻已 升遐矣。余于 阙下哭临。且辞岳丈。即出城入州府。随玄石成服。玄石问窃闻外议。君于今番别荐。必难得免。不知君欲如何自处否。余对曰。闻已不得免矣。然自处之宜。诚未及思量。仍问所以处之之道。玄石曰。一向不出。则必有难处境界。如吾辈所遭可戒也。君有老亲且贫甚。早晚一出。为亲为贫而仕。恐无所害也。盖更化初。户判欲以余论荐。因静能及宋友子徵为余请徐甚力而止云矣。至是复以星变荐人。竟以余首荐。见德涵书。始知之。
余为送岳丈燕行。过先人改题主之礼。然后复入北洞宿。是夜领相临到主家。夜深始归。酒后谈论风生。气像尽好。语及新进名流。似颇歇看。论吴道一曰。此君本来有傲病可闷。盖以其指名侵斥年老台谏。为尤不可也。座中有言赵持谦。倡言吴始寿不可杀者。公曰。不公其心以观罪之轻重。但为后日顾虑为此等议论。此槩不知君臣之义者云。翌日夜。 中宫痘患忽臻危。领相闻报。苍黄借骑其伯氏宅骡子。赴 阙。去路暂入主家。与岳丈相对。只曰。罔极。岳丈亦随往。俄闻已 升遐矣。余于 阙下哭临。且辞岳丈。即出城入州府。随玄石成服。玄石问窃闻外议。君于今番别荐。必难得免。不知君欲如何自处否。余对曰。闻已不得免矣。然自处之宜。诚未及思量。仍问所以处之之道。玄石曰。一向不出。则必有难处境界。如吾辈所遭可戒也。君有老亲且贫甚。早晚一出。为亲为贫而仕。恐无所害也。盖更化初。户判欲以余论荐。因静能及宋友子徵为余请徐甚力而止云矣。至是复以星变荐人。竟以余首荐。见德涵书。始知之。余拜玄石侍宿时。有学子数三人。来学小学。至公明宣语严临下而不毁伤。余问不毁伤何义。玄石答曰。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7H 页
 谓莅下虽严。而不毁伤。其在下人之体肤也。余又问若有罪则杖之。亦当然事也。玄石曰。有罪而杖。何可谓之毁伤也。(以上庚申所录。)
谓莅下虽严。而不毁伤。其在下人之体肤也。余又问若有罪则杖之。亦当然事也。玄石曰。有罪而杖。何可谓之毁伤也。(以上庚申所录。)李挺英士秀。亦在坐讲中庸。问余曰。程子释中字。以不偏不倚。而朱子则兼无过不及而言。然则程子所言。亦指未发之中否。余答曰。不然。程子所言。实兼未发已发言。而不偏不倚字。于未发为尤衬切。故朱子专归之未发。复补以无过不及。以释已发之中也。士秀曰。名篇。本取时中。而程子兼言未发。何也。余答曰。此固然。然所谓时中。必先有未发之中。故谓之如此。此则不但程子然也。朱子亦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其兼举动静。一也。士秀以鄙说。告于玄石。玄石答曰。前欲以程子所说。看作专指时中。此君说亦似。然更容商量也。
余以祀典事禀问。玄石答曰。吾意此事。自是中国所当定制者。设令自我制作。若尤翁当国以定则可也。以今朝廷而其能为此耶。仍以昔年所作祀典说一篇出示矣。且见其所撰费隐说。其说曰。曾以理气分看。今乃觉其皆当以理看。以当然谓之费。所以然谓之隐。余问此说可疑。愚意理之用。即指其流行之用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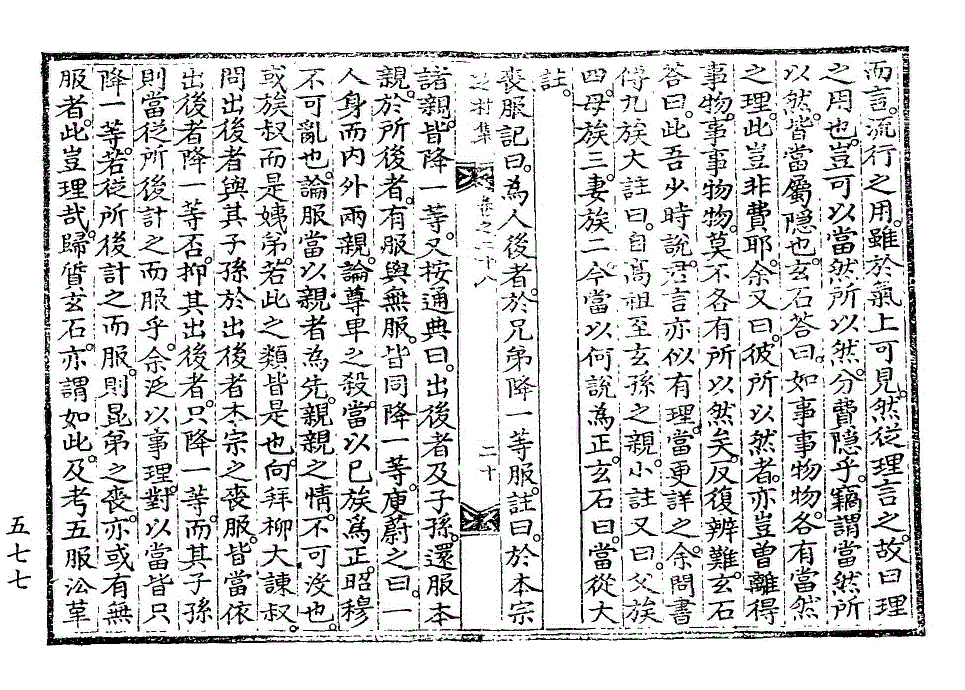 而言。流行之用。虽于气上可见。然从理言之。故曰理之用也。岂可以当然所以然。分费隐乎。窃谓当然所以然。皆当属隐也。玄石答曰。如事事物物。各有当然之理。此岂非费耶。余又曰。彼所以然者。亦岂曾离得事物。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所以然矣。反复辨难。玄石答曰。此吾少时说。君言亦似有理。当更详之。余问书传九族大注曰。自高祖至玄孙之亲。小注又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今当以何说为正。玄石曰。当从大注。
而言。流行之用。虽于气上可见。然从理言之。故曰理之用也。岂可以当然所以然。分费隐乎。窃谓当然所以然。皆当属隐也。玄石答曰。如事事物物。各有当然之理。此岂非费耶。余又曰。彼所以然者。亦岂曾离得事物。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所以然矣。反复辨难。玄石答曰。此吾少时说。君言亦似有理。当更详之。余问书传九族大注曰。自高祖至玄孙之亲。小注又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今当以何说为正。玄石曰。当从大注。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服。注曰。于本宗诸亲。皆降一等。又按通典曰。出后者及子孙。还服本亲。于所后者。有服与无服。皆同降一等。庾蔚之曰。一人身而内外两亲。论尊卑之杀。当以己族为正。昭穆不可乱也。论服当以亲者为先。亲亲之情。不可没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类皆是也。向拜柳大谏叔。问出后者与其子孙于出后者本宗之丧服。皆当依出后者降一等否。抑其出后者。只降一等。而其子孙则当从所后计之而服乎。余泛以事理。对以当皆只降一等。若从所后计之而服。则昆弟之丧。亦或有无服者。此岂理哉。归质玄石。亦谓如此。及考五服沿革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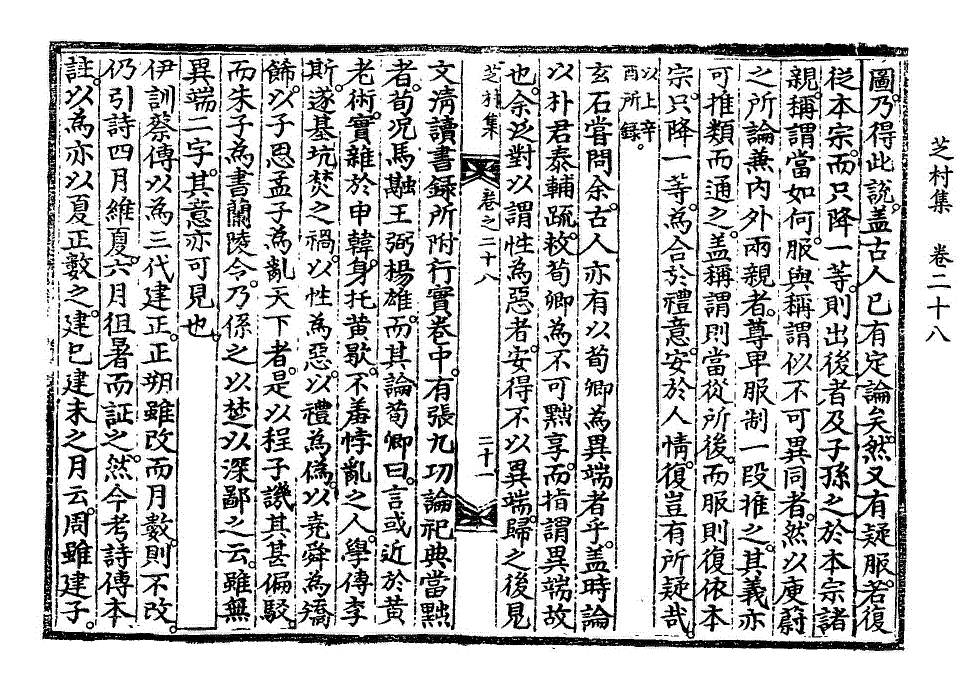 图。乃得此说。盖古人已有定论矣。然又有疑服。若复从本宗。而只降一等。则出后者及子孙之于本宗诸亲。称谓当如何。服与称谓似不可异同者。然以庾蔚之所论兼内外两亲者。尊卑服制一段推之。其义亦可推类而通之。盖称谓则当从所后。而服则复依本宗。只降一等。为合于礼意。安于人情。复岂有所疑哉。(以上辛酉所录。)
图。乃得此说。盖古人已有定论矣。然又有疑服。若复从本宗。而只降一等。则出后者及子孙之于本宗诸亲。称谓当如何。服与称谓似不可异同者。然以庾蔚之所论兼内外两亲者。尊卑服制一段推之。其义亦可推类而通之。盖称谓则当从所后。而服则复依本宗。只降一等。为合于礼意。安于人情。复岂有所疑哉。(以上辛酉所录。)玄石尝问余。古人亦有以荀卿为异端者乎。盖时论以朴君泰辅疏。救荀卿为不可黜享。而指谓异端故也。余泛对以谓性为恶者。安得不以异端。归之后见文清读书录所附行实卷中。有张九功论祀典当黜者。荀况马融王弼扬雄。而其论荀卿曰。言或近于黄老术。实杂于申韩。身托黄歇。不羞悖乱之人。学传李斯。遂基坑焚之祸。以性为恶。以礼为伪。以尧舜为矫饰。以子思孟子为乱天下者。是以程子讥其甚偏驳。而朱子为书兰陵令。乃系之以楚以深鄙之云。虽无异端二字。其意亦可见也。
伊训蔡传以为三代建正。正朔虽改而月数。则不改。仍引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而证之。然今考诗传本注。以为亦以夏正数之。建巳建未之月云。周虽建子。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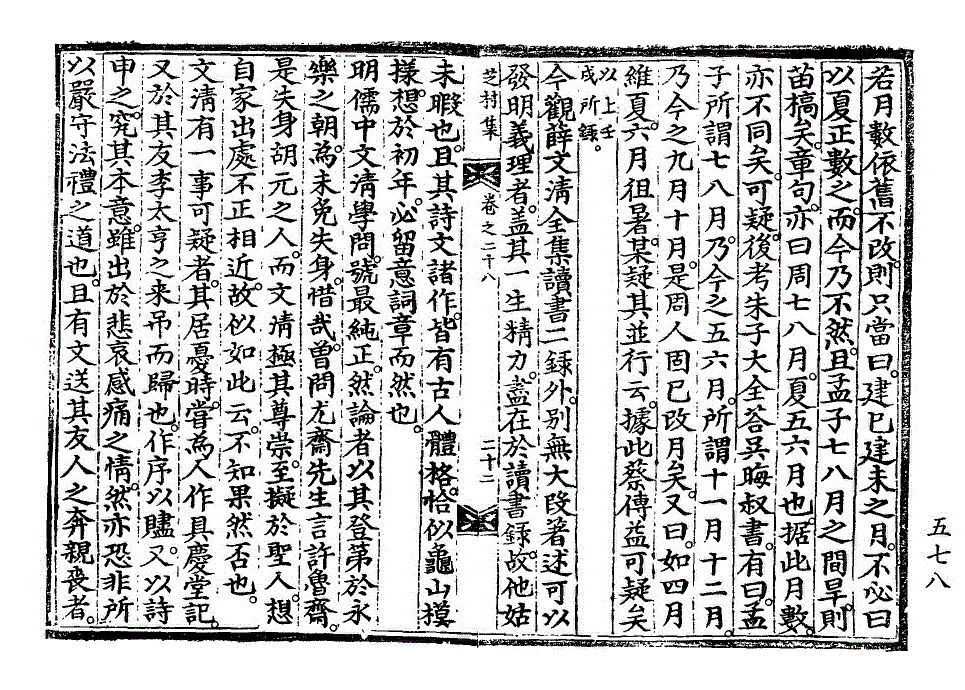 若月数依旧不改。则只当曰。建巳建未之月。不必曰以夏正数之。而今乃不然。且孟子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章句。亦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据此月数。亦不同矣。可疑。后考朱子大全答吴晦叔书。有曰。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又曰。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某疑其并行云。据此蔡传益可疑矣。(以上壬戌所录。)
若月数依旧不改。则只当曰。建巳建未之月。不必曰以夏正数之。而今乃不然。且孟子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章句。亦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据此月数。亦不同矣。可疑。后考朱子大全答吴晦叔书。有曰。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又曰。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某疑其并行云。据此蔡传益可疑矣。(以上壬戌所录。)今观薛文清全集读书二录外。别无大段著述可以发明义理者。盖其一生精力。尽在于读书录。故他姑未暇也。且其诗文诸作。皆有古人体格。恰似龟山模㨾。想于初年。必留意词章而然也。
明儒中文清学问。号最纯正。然论者以其登第于永乐之朝。为未免失身。惜哉。曾问尤斋先生言许鲁斋。是失身胡元之人。而文清极其尊崇。至拟于圣人。想自家出处不正相近。故似如此云。不知果然否也。
文清有一事可疑者。其居忧时。尝为人作具庆堂记。又于其友李太亨之来吊而归也。作序以赆。又以诗申之。究其本意。虽出于悲哀感痛之情。然亦恐非所以严守法礼之道也。且有文送其友人之奔亲丧者。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第 5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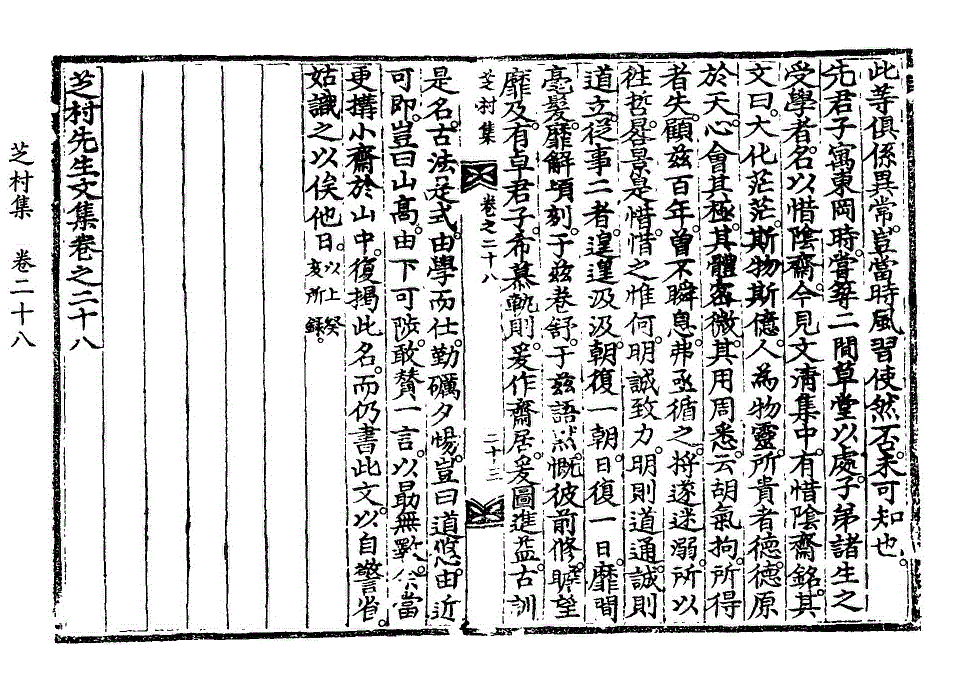 此等俱系异常。岂当时风习使然否。未可知也。
此等俱系异常。岂当时风习使然否。未可知也。先君子寓东冈时。尝筑二间草堂以处。子弟诸生之受学者。名以惜阴斋。今见文清集中。有惜阴斋铭。其文曰。大化茫茫。斯物斯亿。人为物灵。所贵者德。德原于天。心会其极。其体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气拘。所得者失。顾玆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将遂迷溺。所以往哲。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诚致力。明则道通。诚则道立。从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复一朝。日复一日。靡间毫发。靡解顷刻。于玆卷舒。于玆语默。慨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轨则。爰作斋居。爰图进益。古训是名。古法是式。由学而仕。勤砺夕惕。岂曰道悠。由近可即。岂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赞一言。以勖无斁。余当更搆小斋于山中。复揭此名。而仍书此文。以自警省。姑识之以俟他日。(以上癸亥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