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谕告文
谕告文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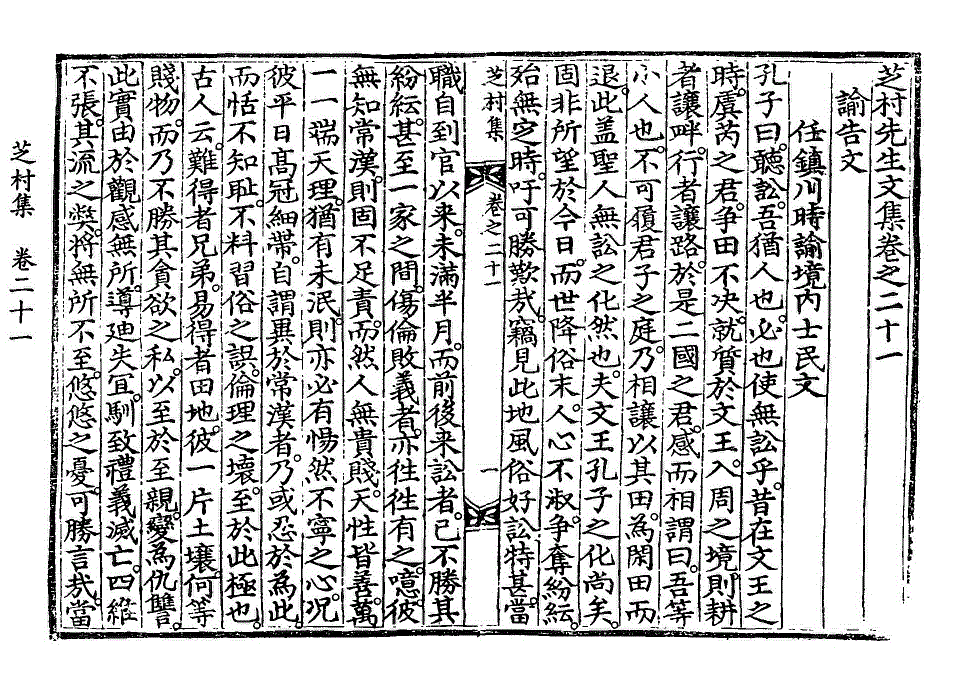 任镇川时谕境内士民文
任镇川时谕境内士民文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昔在文王之时。虞芮之君。争田不决。就质于文王。入周之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于是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吾等小人也。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田。为闲田而退。此盖圣人无讼之化然也。夫文王孔子之化尚矣。固非所望于今日。而世降俗末。人心不淑。争夺纷纭。始无定时。吁可胜叹哉。窃见此地风俗好讼特甚。当职自到官以来。未满半月。而前后来讼者。已不胜其纷纭。甚至一家之间。伤伦败义者。亦往往有之。噫。彼无知常汉。则固不足责。而然人无贵贱。天性皆善。万一一端天理。犹有未泯。则亦必有惕然不宁之心。况彼平日高冠细带。自谓异于常汉者。乃或忍于为此。而恬不知耻。不料习俗之误。伦理之坏。至于此极也。古人云。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彼一片土壤。何等贱物。而乃不胜其贪欲之私。以至于至亲。变为仇雠。此实由于观感无所。导迪失宜。驯致礼义灭亡。四维不张。其流之弊。将无所不至。悠悠之忧。可胜言哉。当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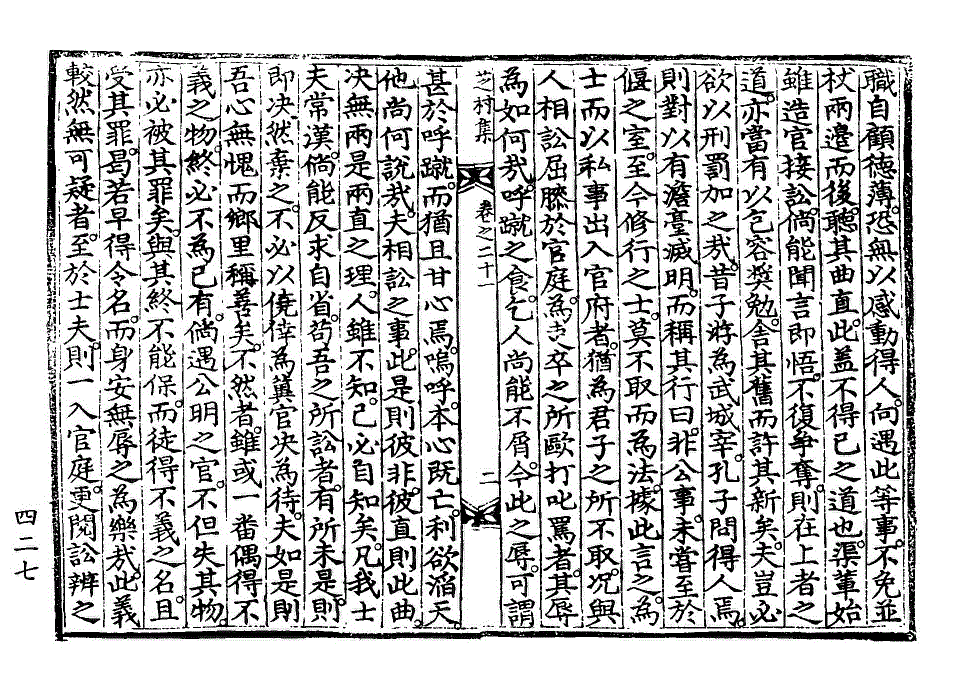 职自顾德薄。恐无以感动得人。向遇此等事。不免并杖两边而后。听其曲直。此盖不得已之道也。渠辈始虽造官接讼。倘能闻言即悟。不复争夺。则在上者之道。亦当有以包容奖勉。舍其旧而许其新矣。夫岂必欲以刑罚加之哉。昔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得人焉。则对以有澹台灭明。而称其行曰。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至今修行之士。莫不取而为法。据此言之。为士而以私事出入官府者。犹为君子之所不取。况与人相讼屈膝于官庭。为吏卒之所欧打叱骂者。其辱为如何哉。呼蹴之食。乞人尚能不屑。今此之辱。可谓甚于呼蹴。而犹且甘心焉。呜呼。本心既亡。利欲滔天。他尚何说哉。夫相讼之事。此是则彼非。彼直则此曲。决无两是两直之理。人虽不知。己必自知矣。凡我士夫常汉。倘能反求自省。苟吾之所讼者。有所未是。则即决然弃之。不必以侥倖为冀官决为待。夫如是则吾心无愧而乡里称善矣。不然者。虽或一番偶得不义之物。终必不为己有。倘遇公明之官。不但失其物。亦必被其罪矣。与其终不能保。而徒得不义之名。且受其罪。曷若早得令名。而身安无辱之为乐哉。此义较然无可疑者。至于士夫。则一入官庭。更阅讼辨之
职自顾德薄。恐无以感动得人。向遇此等事。不免并杖两边而后。听其曲直。此盖不得已之道也。渠辈始虽造官接讼。倘能闻言即悟。不复争夺。则在上者之道。亦当有以包容奖勉。舍其旧而许其新矣。夫岂必欲以刑罚加之哉。昔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得人焉。则对以有澹台灭明。而称其行曰。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至今修行之士。莫不取而为法。据此言之。为士而以私事出入官府者。犹为君子之所不取。况与人相讼屈膝于官庭。为吏卒之所欧打叱骂者。其辱为如何哉。呼蹴之食。乞人尚能不屑。今此之辱。可谓甚于呼蹴。而犹且甘心焉。呜呼。本心既亡。利欲滔天。他尚何说哉。夫相讼之事。此是则彼非。彼直则此曲。决无两是两直之理。人虽不知。己必自知矣。凡我士夫常汉。倘能反求自省。苟吾之所讼者。有所未是。则即决然弃之。不必以侥倖为冀官决为待。夫如是则吾心无愧而乡里称善矣。不然者。虽或一番偶得不义之物。终必不为己有。倘遇公明之官。不但失其物。亦必被其罪矣。与其终不能保。而徒得不义之名。且受其罪。曷若早得令名。而身安无辱之为乐哉。此义较然无可疑者。至于士夫。则一入官庭。更阅讼辨之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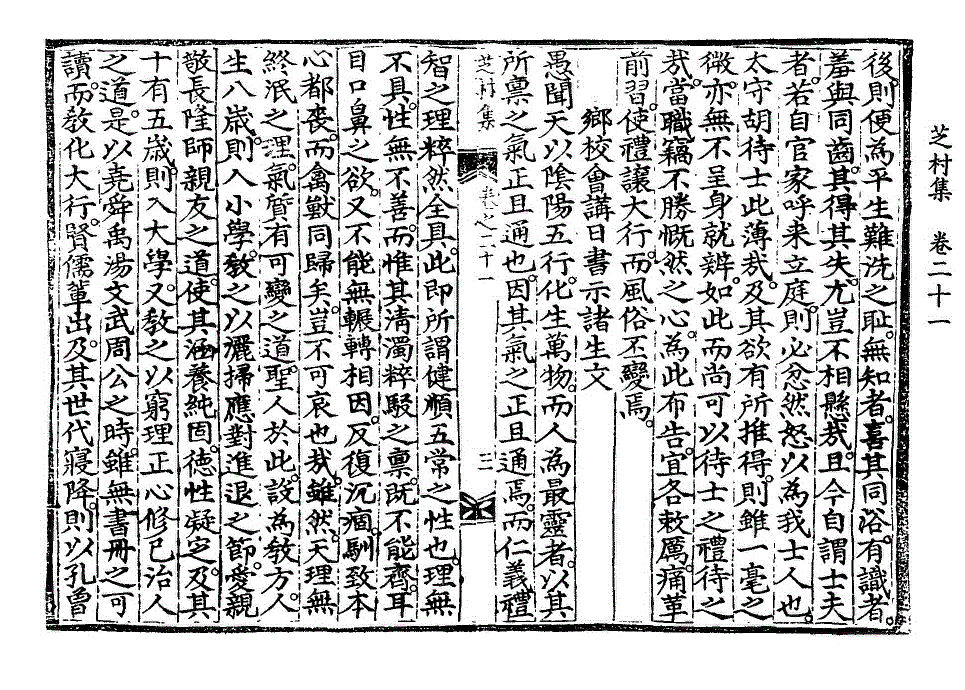 后。则便为平生难洗之耻。无知者。喜其同浴。有识者。羞与同齿。其得其失。尤岂不相悬哉。且今自谓士夫者。若自官家呼来立庭。则必忿然怒以为我士人也。太守胡待士此薄哉。及其欲有所推得。则虽一毫之微。亦无不呈身就辨。如此而尚可以待士之礼待之哉。当职窃不胜慨然之心。为此布告。宜各敕厉。痛革前习。使礼让大行。而风俗丕变焉。
后。则便为平生难洗之耻。无知者。喜其同浴。有识者。羞与同齿。其得其失。尤岂不相悬哉。且今自谓士夫者。若自官家呼来立庭。则必忿然怒以为我士人也。太守胡待士此薄哉。及其欲有所推得。则虽一毫之微。亦无不呈身就辨。如此而尚可以待士之礼待之哉。当职窃不胜慨然之心。为此布告。宜各敕厉。痛革前习。使礼让大行。而风俗丕变焉。乡校会讲日书示诸生文
愚闻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而人为最灵者。以其所禀之气正且通也。因其气之正且通焉。而仁义礼智之理粹然全具。此即所谓健顺五常之性也。理无不具。性无不善。而惟其清浊粹驳之禀。既不能齐。耳目口鼻之欲。又不能无辗转相因。反复沉痼。驯致本心都丧。而禽兽同归矣。岂不可哀也哉。虽然。天理无终泯之理。气质有可变之道。圣人于此。设为教方。人生八岁。则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使其涵养纯固。德性凝定。及其十有五岁。则入大学。又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时。虽无书册之可读。而教化大行。贤儒辈出。及其世代寝降。则以孔曾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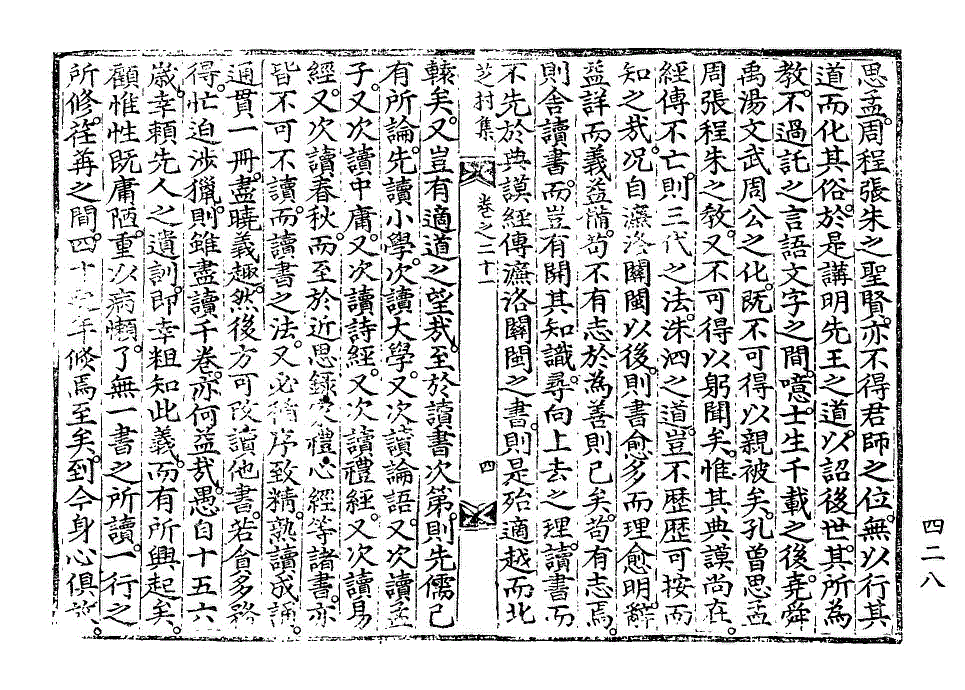 思孟。周程张朱之圣贤。亦不得君师之位。无以行其道而化其俗。于是讲明先王之道。以诏后世。其所为教。不过托之言语文字之间。噫。士生千载之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化。既不可得以亲被矣。孔曾思孟周张程朱之教。又不可得以躬闻矣。惟其典谟尚在。经传不亡。则三代之法。洙泗之道。岂不历历可按而知之哉。况自濂洛关闽以后。则书愈多而理愈明。辞益详而义益备。苟不有志于为善则已矣。苟有志焉。则舍读书。而岂有开其知识。寻向上去之理。读书而不先于典谟经传濂洛关闽之书。则是殆适越而北辕矣。又岂有适道之望哉。至于读书次第。则先儒已有所论。先读小学。次读大学。又次读论语。又次读孟子。又次读中庸。又次读诗经。又次读礼经。又次读易经。又次读春秋。而至于近思录,家礼,心经等诸书。亦皆不可不读。而读书之法。又必循序致精。熟读成诵。通贯一册。尽晓义趣。然后方可改读他书。若贪多务得。忙迫涉猎。则虽尽读千卷。亦何益哉。愚自十五六岁。幸赖先人之遗训。即幸粗知此义。而有所兴起矣。顾惟性既庸陋。重以病懒。了无一书之所读。一行之所修。荏苒之间。四十之年倏焉至矣。到今身心俱放。
思孟。周程张朱之圣贤。亦不得君师之位。无以行其道而化其俗。于是讲明先王之道。以诏后世。其所为教。不过托之言语文字之间。噫。士生千载之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化。既不可得以亲被矣。孔曾思孟周张程朱之教。又不可得以躬闻矣。惟其典谟尚在。经传不亡。则三代之法。洙泗之道。岂不历历可按而知之哉。况自濂洛关闽以后。则书愈多而理愈明。辞益详而义益备。苟不有志于为善则已矣。苟有志焉。则舍读书。而岂有开其知识。寻向上去之理。读书而不先于典谟经传濂洛关闽之书。则是殆适越而北辕矣。又岂有适道之望哉。至于读书次第。则先儒已有所论。先读小学。次读大学。又次读论语。又次读孟子。又次读中庸。又次读诗经。又次读礼经。又次读易经。又次读春秋。而至于近思录,家礼,心经等诸书。亦皆不可不读。而读书之法。又必循序致精。熟读成诵。通贯一册。尽晓义趣。然后方可改读他书。若贪多务得。忙迫涉猎。则虽尽读千卷。亦何益哉。愚自十五六岁。幸赖先人之遗训。即幸粗知此义。而有所兴起矣。顾惟性既庸陋。重以病懒。了无一书之所读。一行之所修。荏苒之间。四十之年倏焉至矣。到今身心俱放。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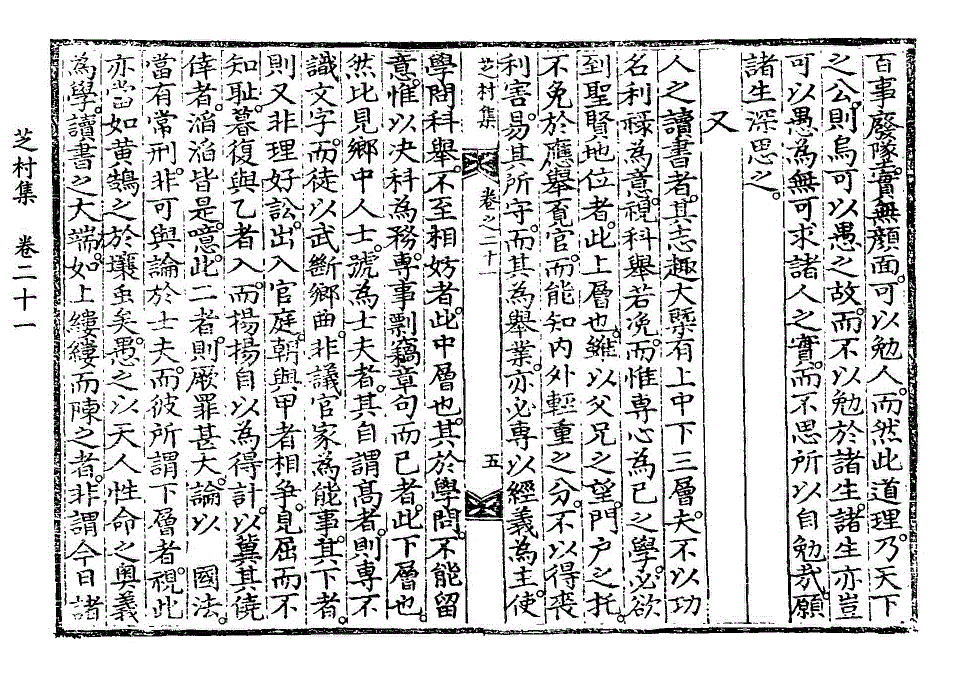 百事废坠。实无颜面。可以勉人。而然此道理。乃天下之公。则乌可以愚之故。而不以勉于诸生。诸生亦岂可以愚为无可求诸人之实。而不思所以自勉哉。愿诸生深思之。
百事废坠。实无颜面。可以勉人。而然此道理。乃天下之公。则乌可以愚之故。而不以勉于诸生。诸生亦岂可以愚为无可求诸人之实。而不思所以自勉哉。愿诸生深思之。乡校会讲日书示诸生文
人之读书者。其志趣大槩有上中下三层。夫不以功名利禄为意。视科举若浼。而惟专心为己之学。必欲到圣贤地位者。此上层也。虽以父兄之望。门户之托。不免于应举觅官。而能知内外轻重之分。不以得丧利害。易其所守。而其为举业。亦必专以经义为主。使学问科举。不至相妨者。此中层也。其于学问。不能留意。惟以决科为务。专事剽窃章句而已者。此下层也。然比见乡中人士。号为士夫者。其自谓高者。则专不识文字。而徒以武断乡曲。非议官家为能事。其下者。则又非理好讼。出入官庭。朝与甲者相争。见屈而不知耻。暮复与乙者入。而扬扬自以为得计。以冀其侥倖者。滔滔皆是。噫。此二者。则厥罪甚大。论以 国法。当有常刑。非可与论于士夫。而彼所谓下层者。视此亦当如黄鹄之于壤虫矣。愚之以天人性命之奥义为学。读书之大端。如上缕缕而陈之者。非谓今日诸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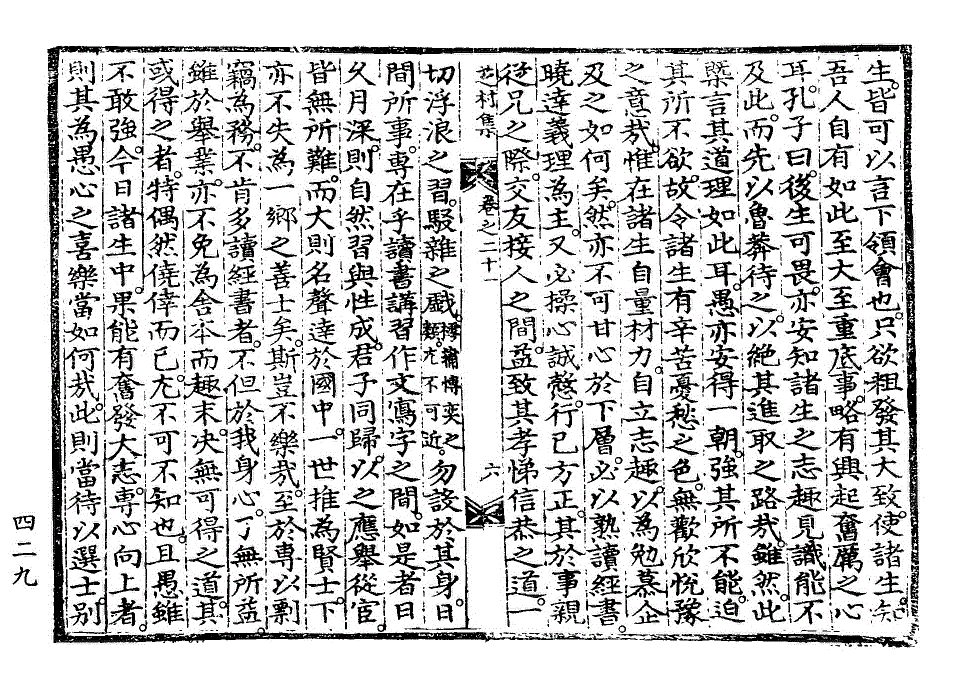 生。皆可以言下领会也。只欲粗发其大致。使诸生。知吾人自有如此至大至重底事。略有兴起奋厉之心耳。孔子曰。后生可畏。亦安知诸生之志趣见识能不及此。而先以鲁莽待之。以绝其进取之路哉。虽然。此槩言其道理如此耳。愚亦安得一朝。强其所不能。迫其所不欲。故令诸生有辛苦忧愁之色。无欢欣悦豫之意哉。惟在诸生自量材力。自立志趣。以为勉慕企及之如何矣。然亦不可甘心于下层。必以熟读经书。晓达义理为主。又必操心诚悫。行己方正。其于事亲从兄之际。交友接人之间。益致其孝悌信恭之道。一切浮浪之习。驳杂之戏。(樗蒱博奕之类。尤不可近。)勿设于其身。日间所事。专在乎读书讲习作文写字之间。如是者日久月深。则自然习与性成。君子同归。以之应举从宦。皆无所难。而大则名声达于国中。一世推为贤士。下亦不失为一乡之善士矣。斯岂不乐哉。至于专以剽窃为务。不肯多读经书者。不但于我身心。了无所益。虽于举业。亦不免为舍本而趣末。决无可得之道。其或得之者。特偶然侥倖而已。尤不可不知也。且愚虽不敢强。今日诸生中。果能有奋发大志。专心向上者。则其为愚心之喜乐当如何哉。此则当待以选士。别
生。皆可以言下领会也。只欲粗发其大致。使诸生。知吾人自有如此至大至重底事。略有兴起奋厉之心耳。孔子曰。后生可畏。亦安知诸生之志趣见识能不及此。而先以鲁莽待之。以绝其进取之路哉。虽然。此槩言其道理如此耳。愚亦安得一朝。强其所不能。迫其所不欲。故令诸生有辛苦忧愁之色。无欢欣悦豫之意哉。惟在诸生自量材力。自立志趣。以为勉慕企及之如何矣。然亦不可甘心于下层。必以熟读经书。晓达义理为主。又必操心诚悫。行己方正。其于事亲从兄之际。交友接人之间。益致其孝悌信恭之道。一切浮浪之习。驳杂之戏。(樗蒱博奕之类。尤不可近。)勿设于其身。日间所事。专在乎读书讲习作文写字之间。如是者日久月深。则自然习与性成。君子同归。以之应举从宦。皆无所难。而大则名声达于国中。一世推为贤士。下亦不失为一乡之善士矣。斯岂不乐哉。至于专以剽窃为务。不肯多读经书者。不但于我身心。了无所益。虽于举业。亦不免为舍本而趣末。决无可得之道。其或得之者。特偶然侥倖而已。尤不可不知也。且愚虽不敢强。今日诸生中。果能有奋发大志。专心向上者。则其为愚心之喜乐当如何哉。此则当待以选士。别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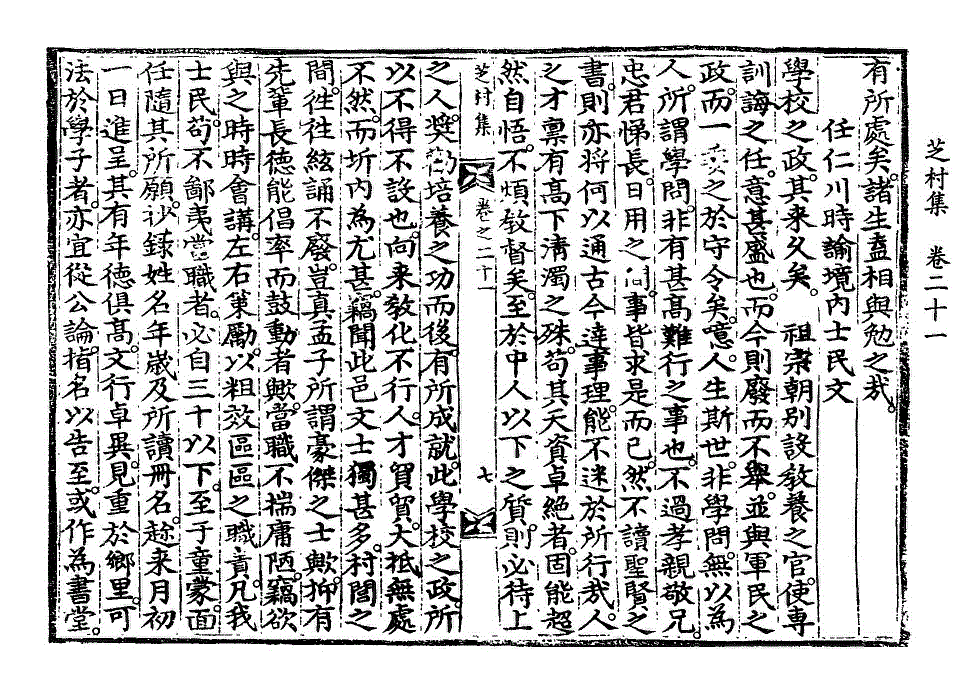 有所处矣。诸生盍相与勉之哉。
有所处矣。诸生盍相与勉之哉。任仁川时谕境内士民文
学校之政。其来久矣。 祖宗朝别设教养之官。使专训诲之任。意甚盛也。而今则废而不举。并与军民之政。而一委之于守令矣。噫。人生斯世。非学问。无以为人。所谓学问。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不过孝亲敬兄。忠君悌长。日用之间。事皆求是而已。然不读圣贤之书。则亦将何以通古今达事理。能不迷于所行哉。人之才禀有高下清浊之殊。苟其天资卓绝者。固能超然自悟。不烦教督矣。至于中人以下之质。则必待上之人。奖劝培养之功而后。有所成就。此学校之政。所以不得不设也。向来教化不行。人才贸贸。大抵无处不然。而圻内为尤甚。窃闻此邑文士独甚多。村闾之间。往往弦诵不废。岂真孟子所谓豪杰之士欤。抑有先辈长德能倡率而鼓动者欤。当职不揣庸陋。窃欲与之时时会讲。左右策励。以粗效区区之职责。凡我士民。苟不鄙夷当职者。必自三十以下。至于童蒙。面任随其所愿。抄录姓名年岁及所读册名。趁来月初一日进呈。其有年德俱高。文行卓异。见重于乡里。可法于学子者。亦宜从公论。指名以告至。或作为书堂。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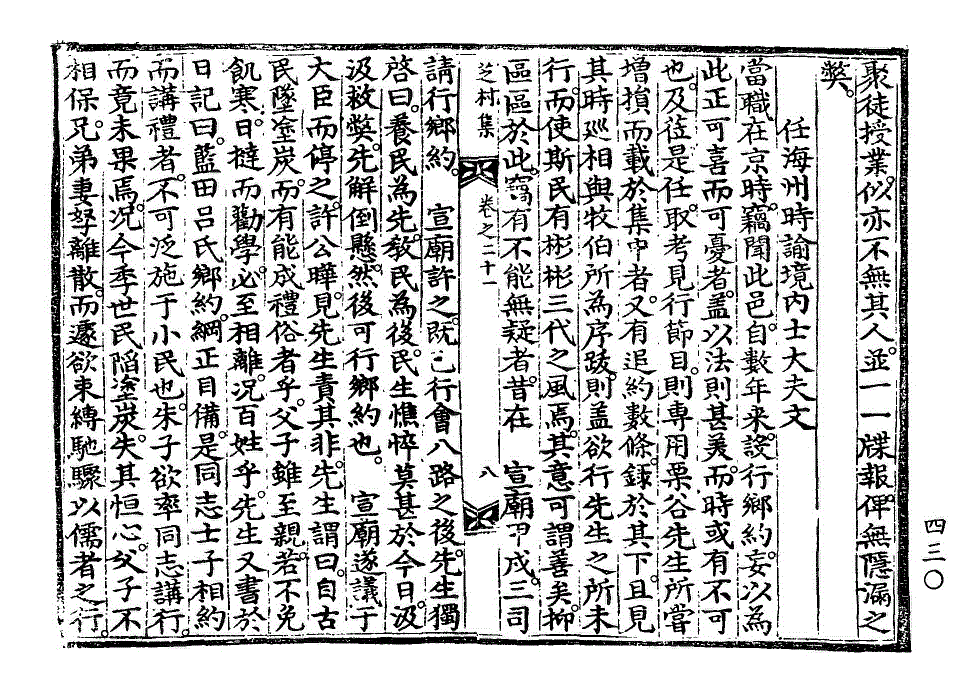 聚徒授业。似亦不无其人。并一一牒报。俾无隐漏之弊。
聚徒授业。似亦不无其人。并一一牒报。俾无隐漏之弊。任海州时谕境内士大夫文
当职在京时。窃闻此邑。自数年来。设行乡约。妄以为此正可喜而可忧者。盖以法则甚美。而时或有不可也。及莅是任。取考见行节目。则专用栗谷先生所尝增损而载于集中者。又有追约数条。录于其下。且见其时巡相与牧伯所为序跋。则盖欲行先生之所未行。而使斯民有彬彬三代之风焉。其意可谓善矣。抑区区于此。窃有不能无疑者。昔在 宣庙甲戌。三司请行乡约。 宣庙许之。既已行会八路之后。先生独启曰。养民为先。教民为后。民生憔悴莫甚于今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悬。然后可行乡约也。 宣庙遂议于大臣而停之。许公晔。见先生责其非。先生谓曰。自古民坠涂炭。而有能成礼俗者乎。父子虽至亲。若不免饥寒。日挞而劝学。必至相离。况百姓乎。先生又书于日记曰。蓝田吕氏乡约。纲正目备。是同志士子相约而讲礼者。不可泛施于小民也。朱子欲率同志讲行。而竟未果焉。况今季世民陷涂炭。失其恒心。父子不相保。兄弟妻孥离散。而遽欲束缚驰骤以儒者之行。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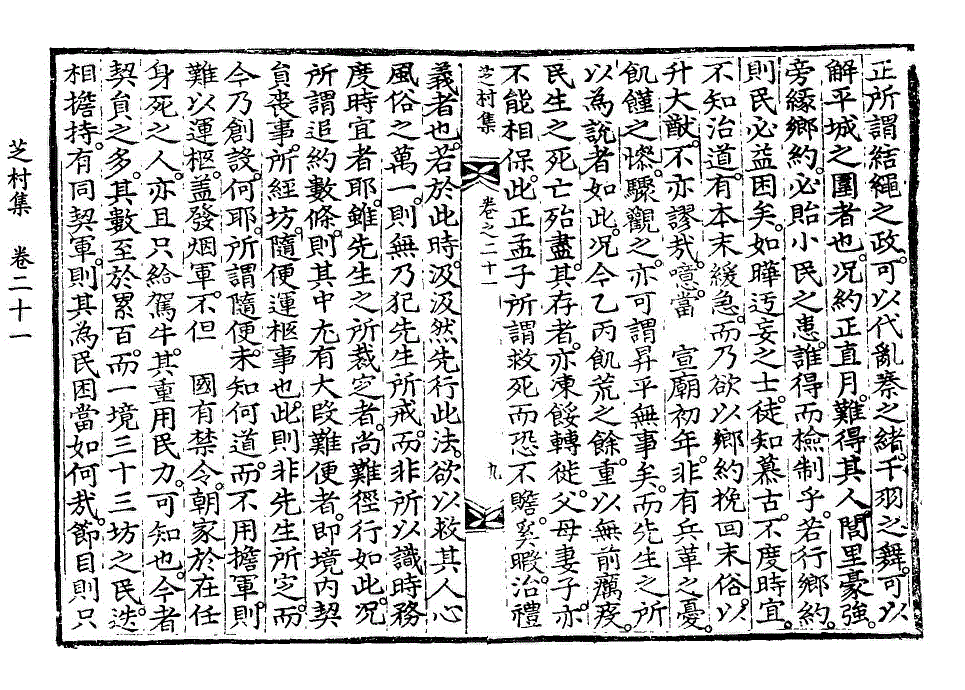 正所谓结绳之政。可以代乱秦之绪。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围者也。况约正直月。难得其人。闾里豪强。旁缘乡约。必贻小民之患。谁得而检制乎。若行乡约。则民必益困矣。如晔迂妄之士。徒知慕古。不度时宜。不知治道。有本末缓急。而乃欲以乡约挽回末俗。以升大猷。不亦谬哉。噫。当 宣庙初年。非有兵革之忧。饥馑之惨。骤观之。亦可谓升平无事矣。而先生之所以为说者如此。况今乙丙饥荒之馀。重以无前疠疫。民生之死亡殆尽。其存者。亦冻馁转徙。父母妻子。亦不能相保。此正孟子所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者也。若于此时。汲汲然先行此法。欲以救其人心风俗之万一。则无乃犯先生所戒。而非所以识时务度时宜者耶。虽先生之所裁定者。尚难径行如此。况所谓追约数条。则其中尤有大段难便者。即境内契员丧事。所经坊。随便运柩事也。此则非先生所定。而今乃创设。何耶。所谓随便。未知何道。而不用担军。则难以运柩。盖发烟军。不但 国有禁令。朝家于在任身死之人。亦且只给驾牛。其重用民力。可知也。今者契员之多。其数至于累百。而一境三十三坊之民。迭相担持。有同契军。则其为民困当如何哉。节目则只
正所谓结绳之政。可以代乱秦之绪。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围者也。况约正直月。难得其人。闾里豪强。旁缘乡约。必贻小民之患。谁得而检制乎。若行乡约。则民必益困矣。如晔迂妄之士。徒知慕古。不度时宜。不知治道。有本末缓急。而乃欲以乡约挽回末俗。以升大猷。不亦谬哉。噫。当 宣庙初年。非有兵革之忧。饥馑之惨。骤观之。亦可谓升平无事矣。而先生之所以为说者如此。况今乙丙饥荒之馀。重以无前疠疫。民生之死亡殆尽。其存者。亦冻馁转徙。父母妻子。亦不能相保。此正孟子所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者也。若于此时。汲汲然先行此法。欲以救其人心风俗之万一。则无乃犯先生所戒。而非所以识时务度时宜者耶。虽先生之所裁定者。尚难径行如此。况所谓追约数条。则其中尤有大段难便者。即境内契员丧事。所经坊。随便运柩事也。此则非先生所定。而今乃创设。何耶。所谓随便。未知何道。而不用担军。则难以运柩。盖发烟军。不但 国有禁令。朝家于在任身死之人。亦且只给驾牛。其重用民力。可知也。今者契员之多。其数至于累百。而一境三十三坊之民。迭相担持。有同契军。则其为民困当如何哉。节目则只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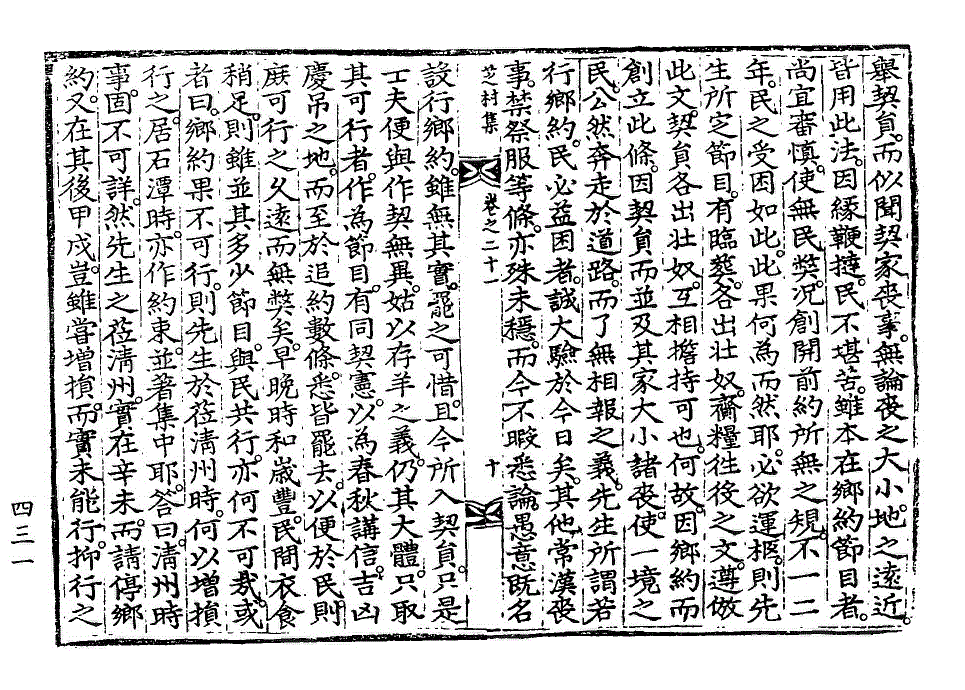 举契员。而似闻契家丧事。无论丧之大小。地之远近。皆用此法。因缘鞭挞。民不堪苦。虽本在乡约节目者。尚宜审慎。使无民弊。况创开前约所无之规。不一二年。民之受困如此。此果何为而然耶。必欲运柩。则先生所定节目。有临葬。各出壮奴。赍粮往役之文。遵仿此文。契员各出壮奴。互相担持可也。何故。因乡约而创立此条。因契员而并及其家大小诸丧。使一境之民。公然奔走于道路。而了无相报之义。先生所谓若行乡约。民必益困者。诚大验于今日矣。其他常汉丧事。禁祭服等条。亦殊未稳。而今不暇悉论。愚意既名设行乡约。虽无其实。罢之可惜。且今所入契员。只是士夫便与作契无异。姑以存羊之义。仍其大体。只取其可行者。作为节目。有同契宪。以为春秋讲信。吉凶庆吊之地。而至于追约数条。悉皆罢去。以便于民。则庶可行之久远而无弊矣。早晚时和岁丰。民间衣食稍足。则虽并其多少节目。与民共行。亦何不可哉。或者曰。乡约果不可行。则先生于莅清州时。何以增损行之。居石潭时。亦作约束。并著集中耶。答曰。清州时事。固不可详。然先生之莅清州。实在辛未。而请停乡约。又在其后甲戌。岂虽尝增损。而实未能行。抑行之
举契员。而似闻契家丧事。无论丧之大小。地之远近。皆用此法。因缘鞭挞。民不堪苦。虽本在乡约节目者。尚宜审慎。使无民弊。况创开前约所无之规。不一二年。民之受困如此。此果何为而然耶。必欲运柩。则先生所定节目。有临葬。各出壮奴。赍粮往役之文。遵仿此文。契员各出壮奴。互相担持可也。何故。因乡约而创立此条。因契员而并及其家大小诸丧。使一境之民。公然奔走于道路。而了无相报之义。先生所谓若行乡约。民必益困者。诚大验于今日矣。其他常汉丧事。禁祭服等条。亦殊未稳。而今不暇悉论。愚意既名设行乡约。虽无其实。罢之可惜。且今所入契员。只是士夫便与作契无异。姑以存羊之义。仍其大体。只取其可行者。作为节目。有同契宪。以为春秋讲信。吉凶庆吊之地。而至于追约数条。悉皆罢去。以便于民。则庶可行之久远而无弊矣。早晚时和岁丰。民间衣食稍足。则虽并其多少节目。与民共行。亦何不可哉。或者曰。乡约果不可行。则先生于莅清州时。何以增损行之。居石潭时。亦作约束。并著集中耶。答曰。清州时事。固不可详。然先生之莅清州。实在辛未。而请停乡约。又在其后甲戌。岂虽尝增损。而实未能行。抑行之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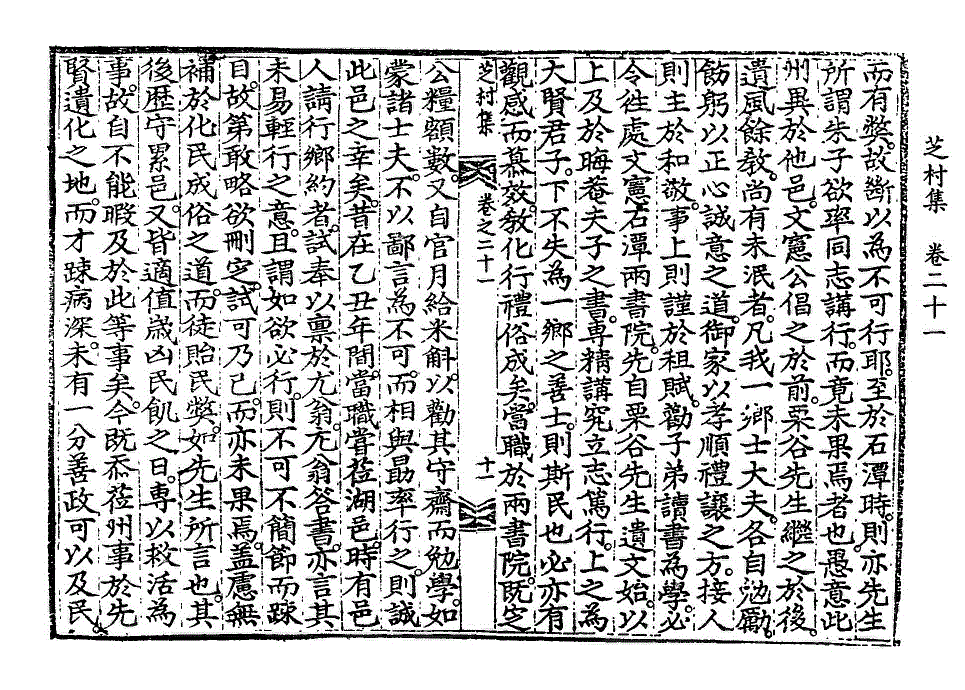 而有弊。故断以为不可行耶。至于石潭时。则亦先生所谓朱子欲率同志讲行。而竟未果焉者也。愚意此州异于他邑。文宪公倡之于前。栗谷先生继之于后。遗风馀教。尚有未泯者。凡我一乡士大夫。各自勉励。饬躬以正心诚意之道。御家以孝顺礼让之方。接人则主于和敬。事上则谨于租赋。劝子弟读书为学。必令往处文宪,石潭两书院。先自栗谷先生遗文始。以上及于晦庵夫子之书。专精讲究立志笃行。上之为大贤君子。下不失为一乡之善士。则斯民也必亦有观感而慕效。教化行礼俗成矣。当职于两书院。既定公粮额数。又自官月给米斛。以劝其守斋而勉学。如蒙诸士夫。不以鄙言为不可。而相与勖率行之。则诚此邑之幸矣。昔在乙丑年间。当职尝莅湖邑。时有邑人请行乡约者。试奉以禀于尤翁。尤翁答书。亦言其未易轻行之意。且谓如欲必行。则不可不简节而疏目。故第敢略欲删定。试可乃已。而亦未果焉。盖虑无补于化民成俗之道。而徒贻民弊。如先生所言也。其后历守累邑。又皆适值岁凶民饥之日。专以救活为事。故自不能暇及于此等事矣。今既忝莅州事于先贤遗化之地。而才疏病深。未有一分善政可以及民。
而有弊。故断以为不可行耶。至于石潭时。则亦先生所谓朱子欲率同志讲行。而竟未果焉者也。愚意此州异于他邑。文宪公倡之于前。栗谷先生继之于后。遗风馀教。尚有未泯者。凡我一乡士大夫。各自勉励。饬躬以正心诚意之道。御家以孝顺礼让之方。接人则主于和敬。事上则谨于租赋。劝子弟读书为学。必令往处文宪,石潭两书院。先自栗谷先生遗文始。以上及于晦庵夫子之书。专精讲究立志笃行。上之为大贤君子。下不失为一乡之善士。则斯民也必亦有观感而慕效。教化行礼俗成矣。当职于两书院。既定公粮额数。又自官月给米斛。以劝其守斋而勉学。如蒙诸士夫。不以鄙言为不可。而相与勖率行之。则诚此邑之幸矣。昔在乙丑年间。当职尝莅湖邑。时有邑人请行乡约者。试奉以禀于尤翁。尤翁答书。亦言其未易轻行之意。且谓如欲必行。则不可不简节而疏目。故第敢略欲删定。试可乃已。而亦未果焉。盖虑无补于化民成俗之道。而徒贻民弊。如先生所言也。其后历守累邑。又皆适值岁凶民饥之日。专以救活为事。故自不能暇及于此等事矣。今既忝莅州事于先贤遗化之地。而才疏病深。未有一分善政可以及民。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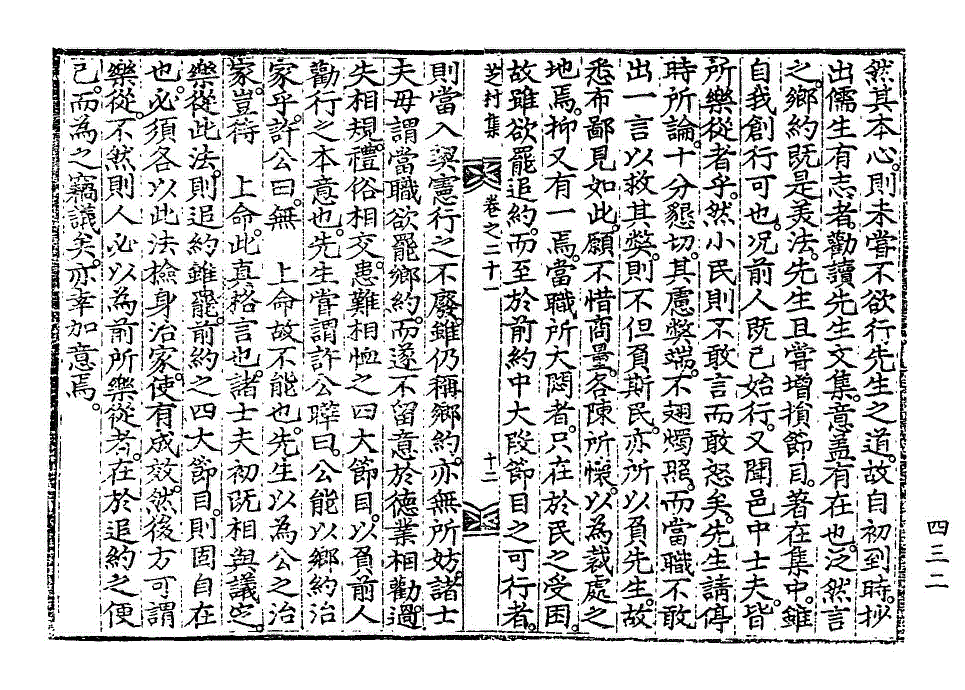 然其本心。则未尝不欲行先生之道。故自初到时。抄出儒生有志者。劝读先生文集。意盖有在也。泛然言之。乡约既是美法。先生且尝增损节目。著在集中。虽自我创行可也。况前人既已始行。又闻邑中士夫。皆所乐从者乎。然小民则不敢言而敢怒矣。先生请停时所论。十分恳切。其虑弊端。不翅烛照。而当职不敢出一言以救其弊。则不但负斯民。亦所以负先生。故悉布鄙见如此。愿不惜商量。各陈所怀。以为裁处之地焉。抑又有一焉。当职所大闷者。只在于民之受困。故虽欲罢追约。而至于前约中大段节目之可行者。则当入契宪行之不废。虽仍称乡约。亦无所妨。诸士夫毋谓当职欲罢乡约。而遂不留意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四大节目。以负前人劝行之本意也。先生尝谓许公晔曰。公能以乡约治家乎。许公曰。无 上命故不能也。先生以为公之治家。岂待 上命。此真格言也。诸士夫初既相与议定。乐从此法。则追约虽罢。前约之四大节目。则固自在也。必须各以此法检身治家。使有成效。然后方可谓乐从。不然则人必以为前所乐从者。在于追约之便已。而为之窃议矣。亦幸加意焉。
然其本心。则未尝不欲行先生之道。故自初到时。抄出儒生有志者。劝读先生文集。意盖有在也。泛然言之。乡约既是美法。先生且尝增损节目。著在集中。虽自我创行可也。况前人既已始行。又闻邑中士夫。皆所乐从者乎。然小民则不敢言而敢怒矣。先生请停时所论。十分恳切。其虑弊端。不翅烛照。而当职不敢出一言以救其弊。则不但负斯民。亦所以负先生。故悉布鄙见如此。愿不惜商量。各陈所怀。以为裁处之地焉。抑又有一焉。当职所大闷者。只在于民之受困。故虽欲罢追约。而至于前约中大段节目之可行者。则当入契宪行之不废。虽仍称乡约。亦无所妨。诸士夫毋谓当职欲罢乡约。而遂不留意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四大节目。以负前人劝行之本意也。先生尝谓许公晔曰。公能以乡约治家乎。许公曰。无 上命故不能也。先生以为公之治家。岂待 上命。此真格言也。诸士夫初既相与议定。乐从此法。则追约虽罢。前约之四大节目。则固自在也。必须各以此法检身治家。使有成效。然后方可谓乐从。不然则人必以为前所乐从者。在于追约之便已。而为之窃议矣。亦幸加意焉。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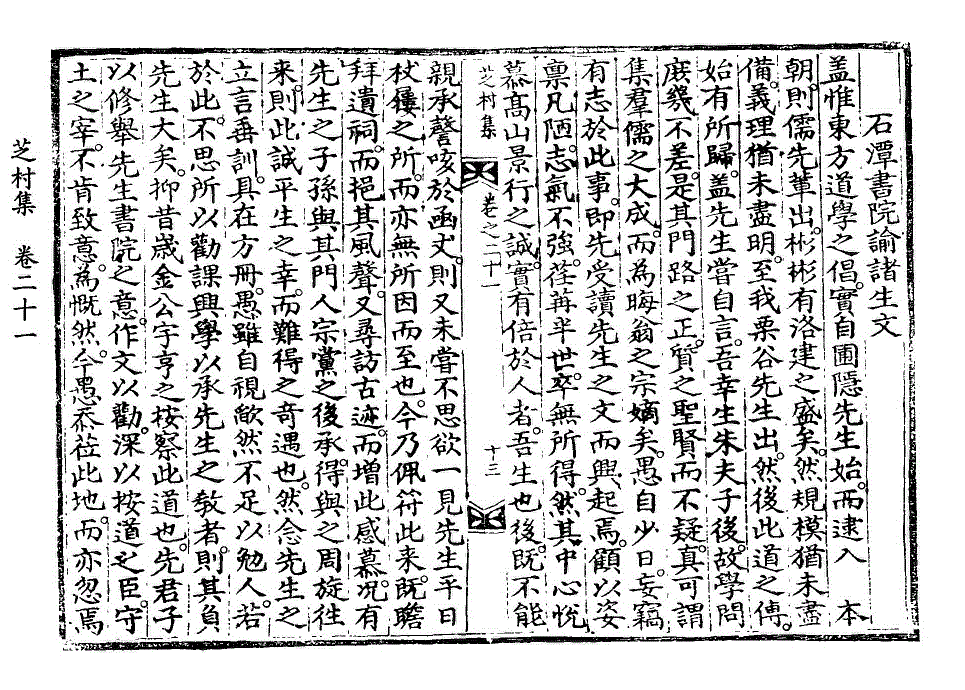 石潭书院谕诸生文
石潭书院谕诸生文盖惟东方道学之倡。实自圃隐先生始。而逮入 本朝。则儒先辈出。彬彬有洛建之盛矣。然规模犹未尽备。义理犹未尽明。至我栗谷先生出。然后此道之传。始有所归。盖先生尝自言。吾幸生朱夫子后。故学问庶几不差。是其门路之正。质之圣贤而不疑。真可谓集群儒之大成。而为晦翁之宗嫡矣。愚自少日。妄窃有志于此事。即先受读先生之文而兴起焉。顾以姿禀凡陋。志气不强。荏苒半世。卒无所得。然其中心悦慕高山景行之诚。实有倍于人者。吾生也后。既不能亲承謦咳于函丈。则又未尝不思欲一见先生平日杖屦之所。而亦无所因而至也。今乃佩符此来。既瞻拜遗祠。而挹其风声。又寻访古迹。而增此感慕。况有先生之子孙与其门人宗党之后承。得与之周旋往来。则此诚平生之幸。而难得之奇遇也。然念先生之立言垂训。具在方册。愚虽自视欿然不足以勉人。若于此。不思所以劝课兴学以承先生之教者。则其负先生大矣。抑昔岁金公宇亨之按察此道也。先君子以修举先生书院之意。作文以劝。深以按道之臣。守土之宰。不肯致意。为慨然。今愚忝莅此地。而亦忽焉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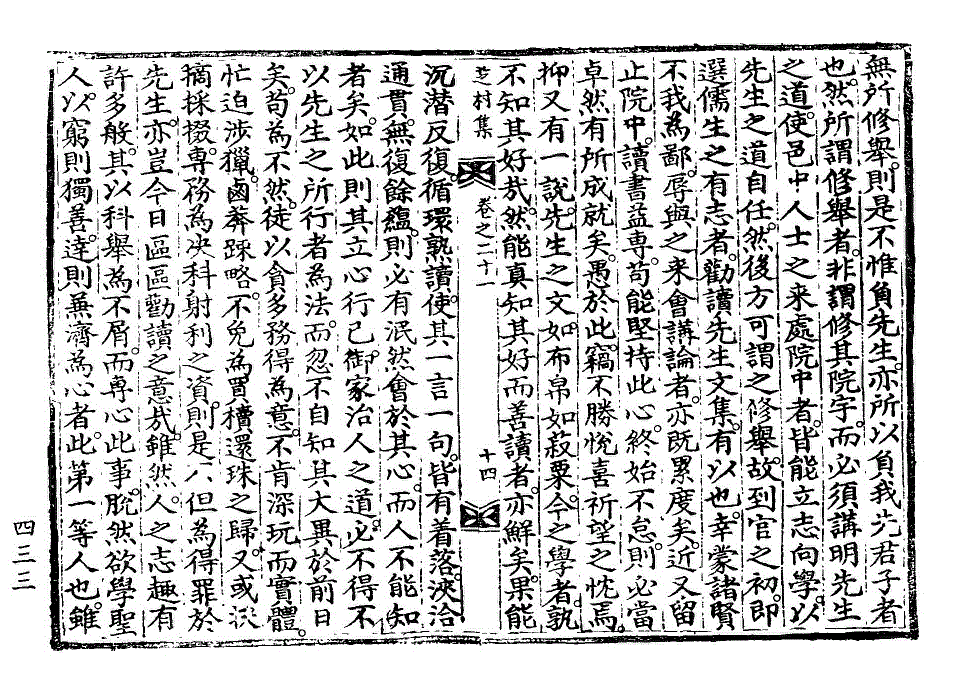 无所修举。则是不惟负先生。亦所以负我先君子者也。然所谓修举者。非谓修其院宇。而必须讲明先生之道。使邑中人士之来处院中者。皆能立志向学。以先生之道自任。然后方可谓之修举。故到官之初。即选儒生之有志者。劝读先生文集。有以也。幸蒙诸贤不我为鄙。辱与之来会讲论者。亦既累度矣。近又留止院中。读书益专。苟能坚持此心。终始不怠。则必当卓然有所成就矣。愚于此。窃不胜悦喜祈望之忱焉。抑又有一说。先生之文。如布帛如菽粟。今之学者。孰不知其好哉。然能真知其好而善读者。亦鲜矣。果能沉潜反复。循环熟读。使其一言一句。皆有着落。浃洽通贯。无复馀蕴。则必有泯然会于其心。而人不能知者矣。如此则其立心行己。御家治人之道。必不得不以先生之所行者为法。而忽不自知其大异于前日矣。苟为不然。徒以贪多务得为意。不肯深玩而实体。忙迫涉猎。卤莽疏略。不免为买椟还珠之归。又或抉摘采掇。专务为决科射利之资。则是不但为得罪于先生。亦岂今日区区劝读之意哉。虽然。人之志趣有许多般。其以科举为不屑。而专心此事。脱然欲学圣人。以穷则独善。达则兼济为心者。此第一等人也。虽
无所修举。则是不惟负先生。亦所以负我先君子者也。然所谓修举者。非谓修其院宇。而必须讲明先生之道。使邑中人士之来处院中者。皆能立志向学。以先生之道自任。然后方可谓之修举。故到官之初。即选儒生之有志者。劝读先生文集。有以也。幸蒙诸贤不我为鄙。辱与之来会讲论者。亦既累度矣。近又留止院中。读书益专。苟能坚持此心。终始不怠。则必当卓然有所成就矣。愚于此。窃不胜悦喜祈望之忱焉。抑又有一说。先生之文。如布帛如菽粟。今之学者。孰不知其好哉。然能真知其好而善读者。亦鲜矣。果能沉潜反复。循环熟读。使其一言一句。皆有着落。浃洽通贯。无复馀蕴。则必有泯然会于其心。而人不能知者矣。如此则其立心行己。御家治人之道。必不得不以先生之所行者为法。而忽不自知其大异于前日矣。苟为不然。徒以贪多务得为意。不肯深玩而实体。忙迫涉猎。卤莽疏略。不免为买椟还珠之归。又或抉摘采掇。专务为决科射利之资。则是不但为得罪于先生。亦岂今日区区劝读之意哉。虽然。人之志趣有许多般。其以科举为不屑。而专心此事。脱然欲学圣人。以穷则独善。达则兼济为心者。此第一等人也。虽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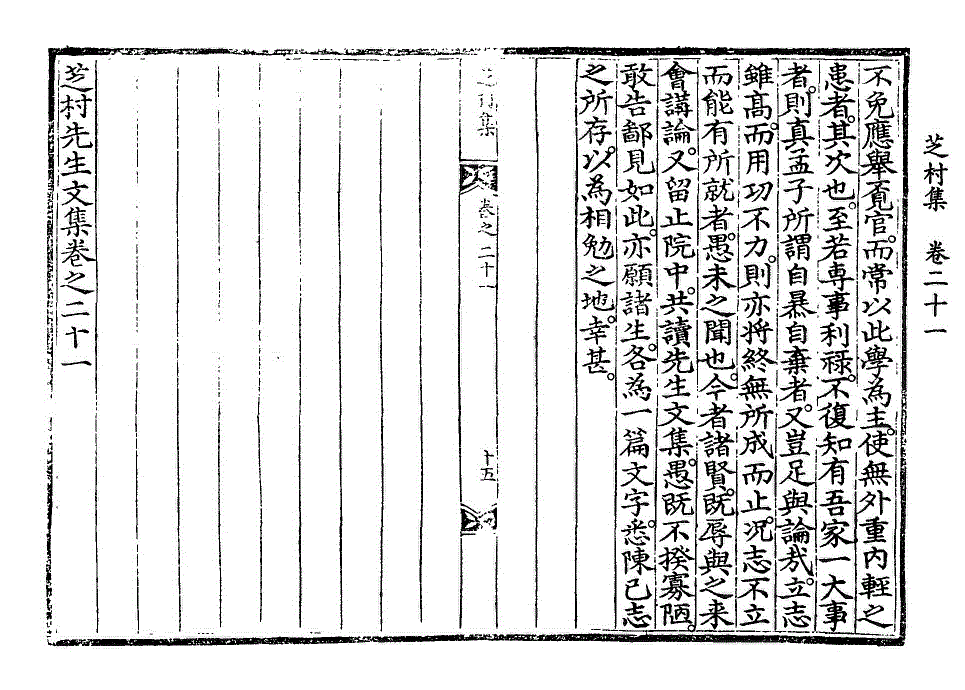 不免应举觅官。而常以此学为主。使无外重内轻之患者。其次也。至若专事利禄。不复知有吾家一大事者。则真孟子所谓自暴自弃者。又岂足与论哉。立志虽高。而用功不力。则亦将终无所成而止。况志不立而能有所就者。愚未之闻也。今者诸贤。既辱与之来会讲论。又留止院中。共读先生文集。愚既不揆寡陋。敢告鄙见如此。亦愿诸生。各为一篇文字。悉陈己志之所存。以为相勉之地。幸甚。
不免应举觅官。而常以此学为主。使无外重内轻之患者。其次也。至若专事利禄。不复知有吾家一大事者。则真孟子所谓自暴自弃者。又岂足与论哉。立志虽高。而用功不力。则亦将终无所成而止。况志不立而能有所就者。愚未之闻也。今者诸贤。既辱与之来会讲论。又留止院中。共读先生文集。愚既不揆寡陋。敢告鄙见如此。亦愿诸生。各为一篇文字。悉陈己志之所存。以为相勉之地。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