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书
书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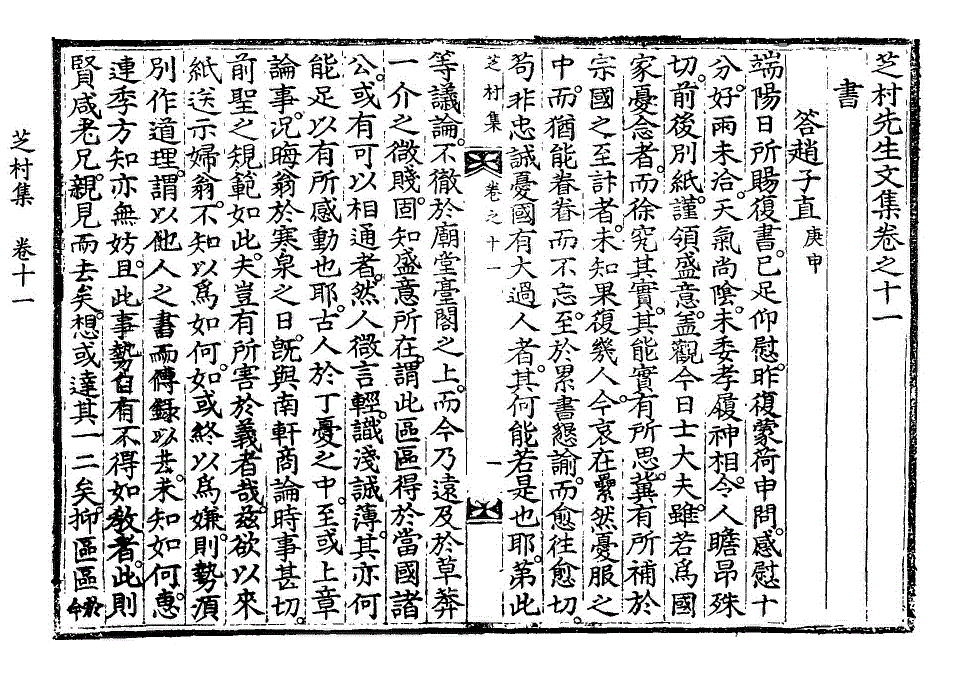 答赵子直(庚申)
答赵子直(庚申)端阳日所赐复书。已足仰慰。昨复蒙荷申问。感慰十分。好雨未洽。天气尚阴。未委孝履神相。令人瞻昂殊切。前后别纸。谨领盛意。盖观今日士大夫。虽若为国家忧念者。而徐究其实。其能实有所思。冀有所补于宗国之至计者。未知果复几人。今哀在累然忧服之中。而犹能眷眷而不忘。至于累书恳谕。而愈往愈切。苟非忠诚忧国有大过人者。其何能若是也耶。第此等议论。不彻于庙堂台阁之上。而今乃远及于草莽一介之微贱。固知盛意所在。谓此区区得于当国诸公。或有可以相通者。然人微言轻。识浅诚薄。其亦何能足以有所感动也耶。古人于丁忧之中。至或上章论事。况晦翁于寒泉之日。既与南轩商论时事甚切。前圣之规范如此。夫岂有所害于义者哉。玆欲以来纸送示妇翁。不知以为如何。如或终以为嫌。则势须别作道理。谓以他人之书而传录以去。未知如何。惠连季方知亦无妨。且此事势自有不得如教者。此则贤咸老兄。亲见而去矣。想或达其一二矣。抑区区于今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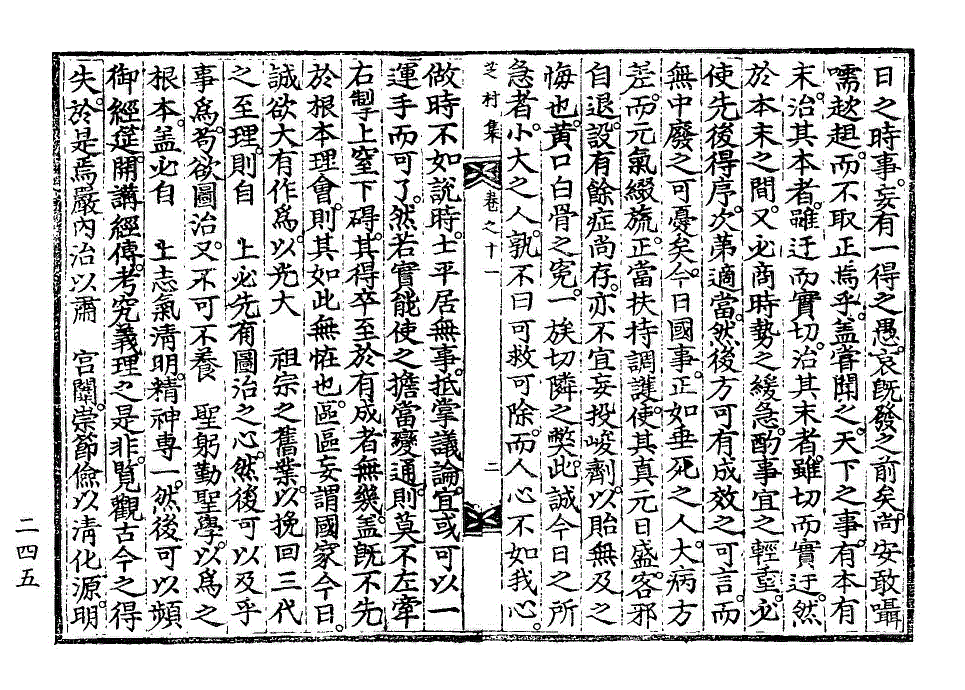 日之时事。妄有一得之愚。哀既发之前矣。尚安敢嗫嚅趑趄。而不取正焉乎。盖尝闻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治其本者。虽迂而实切。治其末者。虽切而实迂。然于本末之间。又必商时势之缓急。酌事宜之轻重。必使先后得序。次第适当。然后方可有成效之可言。而无中废之可忧矣。今日国事。正如垂死之人。大病方差。而元气缀旒。正当扶持调护。使其真元日盛。客邪自退。设有馀症尚存。亦不宜妄投峻剂。以贻无及之悔也。黄口白骨之冤。一族切邻之弊。此诚今日之所急者。小大之人。孰不曰可救可除。而人心不如我心。做时不如说时。士平居无事。抵掌议论。宜或可以一运手而可了。然若实能使之担当变通。则莫不左牵右掣上窒下碍。其得卒至于有成者无几。盖既不先于根本理会。则其如此无怪也。区区妄谓国家今日。诚欲大有作为。以光大 祖宗之旧业。以挽回三代之至理。则自 上必先有图治之心。然后可以及乎事为。苟欲图治。又不可不养 圣躬勤圣学。以为之根本。盖必自 上志气清明。精神专一。然后可以频御经筵。开讲经传。考究义理之是非。览观古今之得失。于是焉严内治以肃 宫闱。崇节俭以清化源。明
日之时事。妄有一得之愚。哀既发之前矣。尚安敢嗫嚅趑趄。而不取正焉乎。盖尝闻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治其本者。虽迂而实切。治其末者。虽切而实迂。然于本末之间。又必商时势之缓急。酌事宜之轻重。必使先后得序。次第适当。然后方可有成效之可言。而无中废之可忧矣。今日国事。正如垂死之人。大病方差。而元气缀旒。正当扶持调护。使其真元日盛。客邪自退。设有馀症尚存。亦不宜妄投峻剂。以贻无及之悔也。黄口白骨之冤。一族切邻之弊。此诚今日之所急者。小大之人。孰不曰可救可除。而人心不如我心。做时不如说时。士平居无事。抵掌议论。宜或可以一运手而可了。然若实能使之担当变通。则莫不左牵右掣上窒下碍。其得卒至于有成者无几。盖既不先于根本理会。则其如此无怪也。区区妄谓国家今日。诚欲大有作为。以光大 祖宗之旧业。以挽回三代之至理。则自 上必先有图治之心。然后可以及乎事为。苟欲图治。又不可不养 圣躬勤圣学。以为之根本。盖必自 上志气清明。精神专一。然后可以频御经筵。开讲经传。考究义理之是非。览观古今之得失。于是焉严内治以肃 宫闱。崇节俭以清化源。明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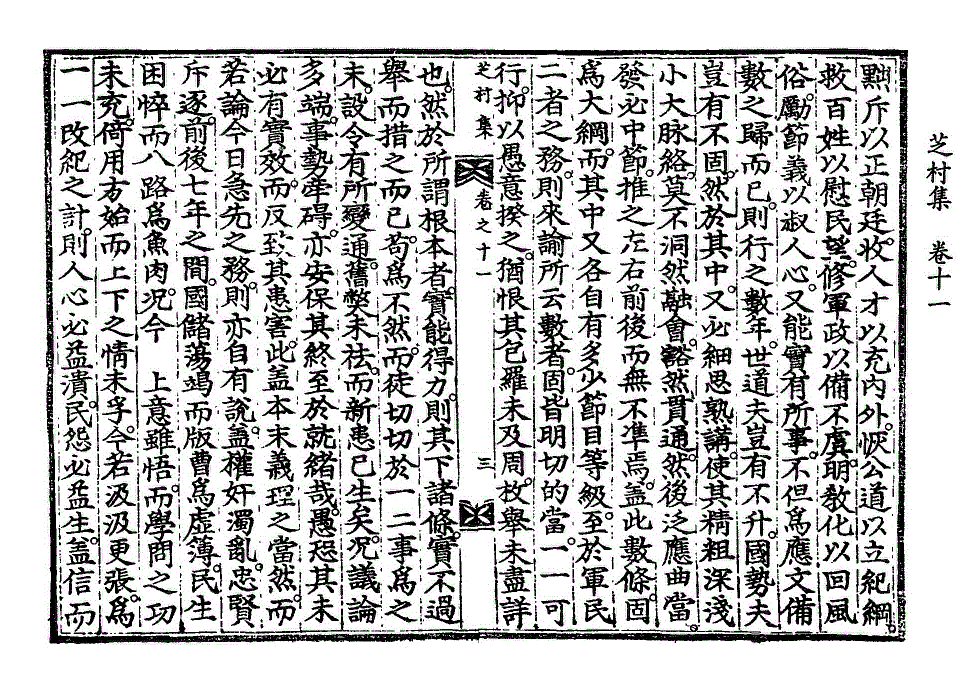 黜斥以正朝廷。收人才以充内外。恢公道以立纪纲。救百姓以慰民望。修军政以备不虞。明教化以回风俗。励节义以淑人心。又能实有所事。不但为应文备数之归而已。则行之数年。世道夫岂有不升。国势夫岂有不固。然于其中。又必细思熟讲。使其精粗深浅小大脉络。莫不洞然融会。豁然贯通。然后泛应曲当。发必中节。推之左右前后而无不准焉。盖此数条。固为大纲。而其中又各自有多少节目等级。至于军民二者之务。则来谕所云数者。固皆明切的当。一一可行。抑以愚意揆之。犹恨其包罗未及周。枚举未尽详也。然于所谓根本者。实能得力。则其下诸条。实不过举而措之而已。苟为不然。而徒切切于一二事为之末。设令有所变通。旧弊未祛。而新患已生矣。况议论多端。事势牵碍。亦安保其终至于就绪哉。愚恐其未必有实效。而反致其患害。此盖本末义理之当然。而若论今日急先之务。则亦自有说。盖权奸浊乱。忠贤斥逐。前后七年之间。国储荡竭而版曹为虚簿。民生困悴而八路为鱼肉。况今 上意虽悟。而学问之功未充。倚用方始而上下之情未孚。今若汲汲更张。为一一改纪之计。则人心必益溃。民怨必益生。盖信而
黜斥以正朝廷。收人才以充内外。恢公道以立纪纲。救百姓以慰民望。修军政以备不虞。明教化以回风俗。励节义以淑人心。又能实有所事。不但为应文备数之归而已。则行之数年。世道夫岂有不升。国势夫岂有不固。然于其中。又必细思熟讲。使其精粗深浅小大脉络。莫不洞然融会。豁然贯通。然后泛应曲当。发必中节。推之左右前后而无不准焉。盖此数条。固为大纲。而其中又各自有多少节目等级。至于军民二者之务。则来谕所云数者。固皆明切的当。一一可行。抑以愚意揆之。犹恨其包罗未及周。枚举未尽详也。然于所谓根本者。实能得力。则其下诸条。实不过举而措之而已。苟为不然。而徒切切于一二事为之末。设令有所变通。旧弊未祛。而新患已生矣。况议论多端。事势牵碍。亦安保其终至于就绪哉。愚恐其未必有实效。而反致其患害。此盖本末义理之当然。而若论今日急先之务。则亦自有说。盖权奸浊乱。忠贤斥逐。前后七年之间。国储荡竭而版曹为虚簿。民生困悴而八路为鱼肉。况今 上意虽悟。而学问之功未充。倚用方始而上下之情未孚。今若汲汲更张。为一一改纪之计。则人心必益溃。民怨必益生。盖信而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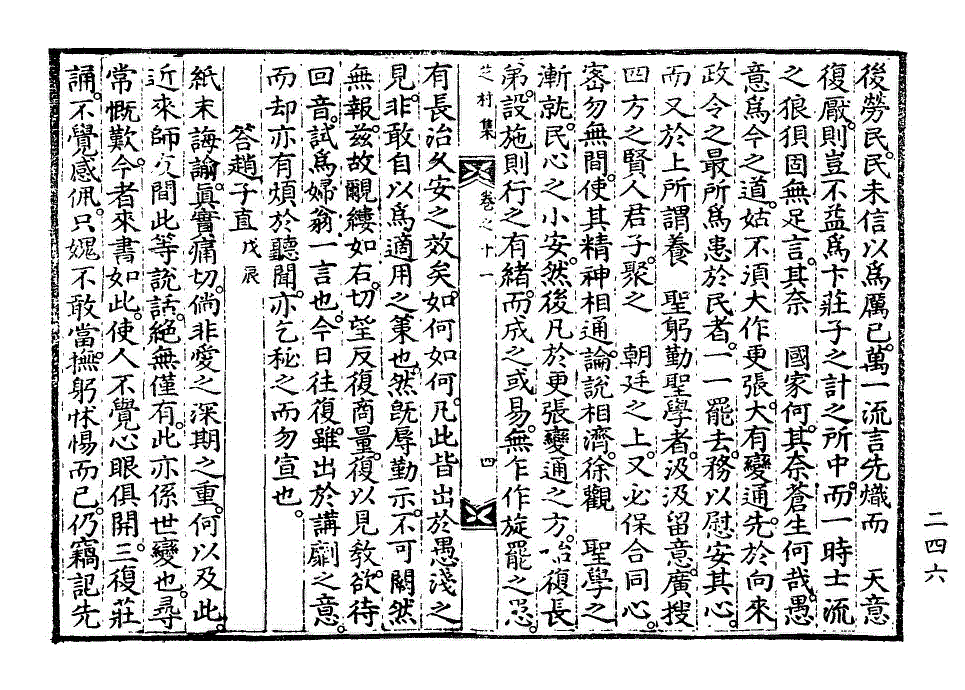 后劳民。民未信以为厉己。万一流言先炽而 天意复厌。则岂不益为卞庄子之计之所中。而一时士流之狼狈固无足言。其奈 国家何。其奈苍生何哉。愚意为今之道。姑不须大作更张。大有变通。先于向来政令之最所为患于民者。一一罢去。务以慰安其心。而又于上所谓养 圣躬勤圣学者。汲汲留意。广搜四方之贤人君子。聚之 朝廷之上。又必保合同心。密勿无间。使其精神相通。论说相济。徐观 圣学之渐就。民心之小安。然后凡于更张变通之方。始复长弟。设施则行之有绪。而成之或易。无乍作旋罢之患。有长治久安之效矣。如何如何。凡此皆出于愚浅之见。非敢自以为适用之策也。然既辱勤示。不可阙然无报。玆故覼缕如右。切望反复商量。复以见教。欲待回音。试为妇翁一言也。今日往复。虽出于讲劘之意。而却亦有烦于听闻。亦乞秘之而勿宣也。
后劳民。民未信以为厉己。万一流言先炽而 天意复厌。则岂不益为卞庄子之计之所中。而一时士流之狼狈固无足言。其奈 国家何。其奈苍生何哉。愚意为今之道。姑不须大作更张。大有变通。先于向来政令之最所为患于民者。一一罢去。务以慰安其心。而又于上所谓养 圣躬勤圣学者。汲汲留意。广搜四方之贤人君子。聚之 朝廷之上。又必保合同心。密勿无间。使其精神相通。论说相济。徐观 圣学之渐就。民心之小安。然后凡于更张变通之方。始复长弟。设施则行之有绪。而成之或易。无乍作旋罢之患。有长治久安之效矣。如何如何。凡此皆出于愚浅之见。非敢自以为适用之策也。然既辱勤示。不可阙然无报。玆故覼缕如右。切望反复商量。复以见教。欲待回音。试为妇翁一言也。今日往复。虽出于讲劘之意。而却亦有烦于听闻。亦乞秘之而勿宣也。答赵子直(戊辰)
纸末诲谕。真实痛切。倘非爱之深期之重。何以及此。近来师友间此等说话。绝无仅有。此亦系世变也。寻常慨叹。今者来书如此。使人不觉心眼俱开。三复庄诵。不觉感佩。只愧不敢当。抚躬怵惕而已。仍窃记先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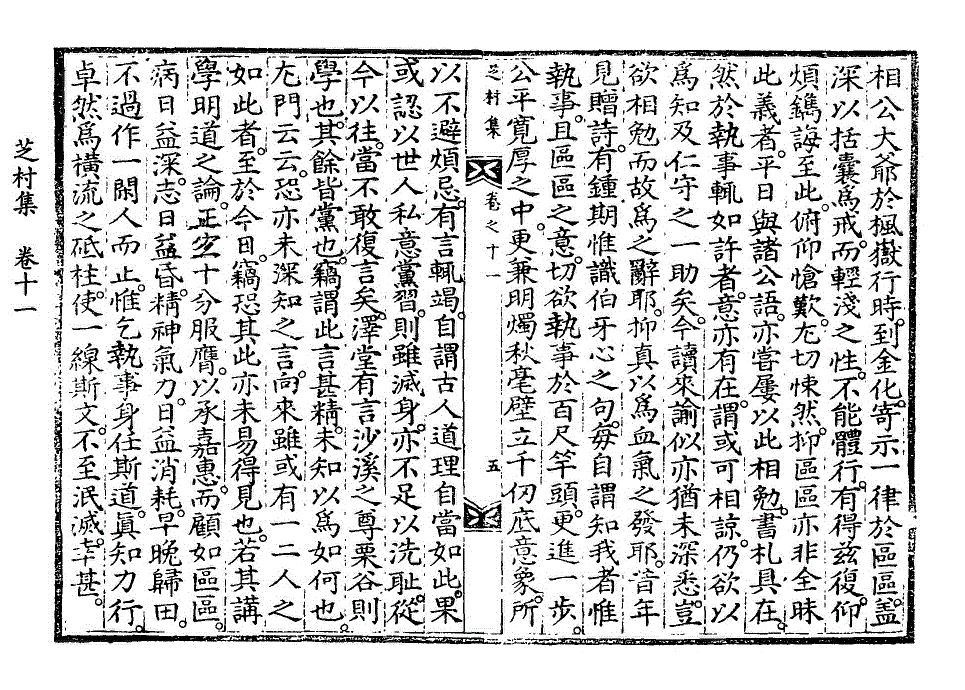 相公大爷于枫岳行时。到金化。寄示一律于区区。盖深以括囊为戒。而轻浅之性。不能体行。有得玆复。仰烦镌诲至此。俯仰怆叹。尤切悚然。抑区区亦非全昧此义者。平日与诸公语。亦尝屡以此相勉。书札具在。然于执事辄如许者。意亦有在。谓或可相谅。仍欲以为知及仁守之一助矣。今读来谕似亦犹未深悉。岂欲相勉而故为之辞耶。抑真以为血气之发耶。昔年见赠诗。有钟期惟识伯牙心之句。每自谓知我者惟执事。且区区之意。切欲执事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公平宽厚之中。更兼明烛秋毫壁立千仞底意象。所以不避烦忌。有言辄竭。自谓古人道理自当如此。果或认以世人私意党习。则虽灭身。亦不足以洗耻。从今以往。当不敢复言矣。泽堂有言沙溪之尊栗谷则学也。其馀皆党也。窃谓此言甚精。未知以为如何也。尤门云云。恐亦未深知之言。向来虽或有一二人之如此者。至于今日。窃恐其此亦未易得见也。若其讲学明道之论。正宜十分服膺。以承嘉惠。而顾如区区。病日益深。志日益昏。精神气力。日益消耗。早晚归田。不过作一闲人而止。惟乞执事身任斯道。真知力行。卓然为横流之砥柱。使一线斯文。不至泯灭。幸甚。
相公大爷于枫岳行时。到金化。寄示一律于区区。盖深以括囊为戒。而轻浅之性。不能体行。有得玆复。仰烦镌诲至此。俯仰怆叹。尤切悚然。抑区区亦非全昧此义者。平日与诸公语。亦尝屡以此相勉。书札具在。然于执事辄如许者。意亦有在。谓或可相谅。仍欲以为知及仁守之一助矣。今读来谕似亦犹未深悉。岂欲相勉而故为之辞耶。抑真以为血气之发耶。昔年见赠诗。有钟期惟识伯牙心之句。每自谓知我者惟执事。且区区之意。切欲执事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公平宽厚之中。更兼明烛秋毫壁立千仞底意象。所以不避烦忌。有言辄竭。自谓古人道理自当如此。果或认以世人私意党习。则虽灭身。亦不足以洗耻。从今以往。当不敢复言矣。泽堂有言沙溪之尊栗谷则学也。其馀皆党也。窃谓此言甚精。未知以为如何也。尤门云云。恐亦未深知之言。向来虽或有一二人之如此者。至于今日。窃恐其此亦未易得见也。若其讲学明道之论。正宜十分服膺。以承嘉惠。而顾如区区。病日益深。志日益昏。精神气力。日益消耗。早晚归田。不过作一闲人而止。惟乞执事身任斯道。真知力行。卓然为横流之砥柱。使一线斯文。不至泯灭。幸甚。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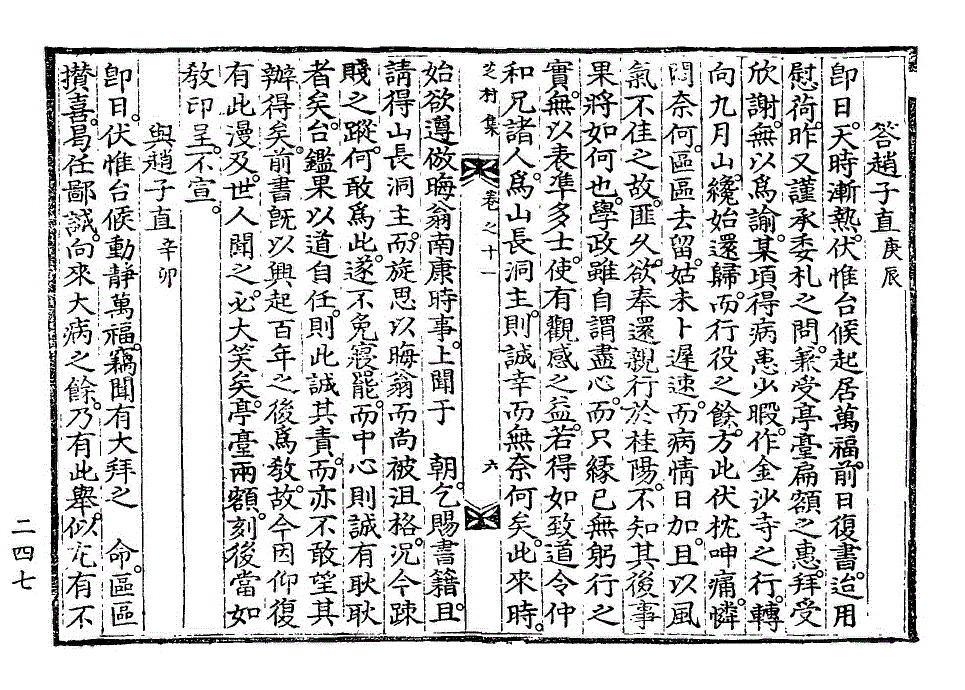 答赵子直(庚辰)
答赵子直(庚辰)即日。天时渐热。伏惟台候起居万福。前日复书。迨用慰荷。昨又谨承委札之问。兼受亭台扁额之惠。拜受欣谢。无以为谕。某顷得病患少暇。作金沙寺之行。转向九月山。才始还归。而行役之馀。方此伏枕呻痛。怜闷奈何。区区去留。姑未卜迟速。而病情日加。且以风气不佳之故。匪久。欲奉还亲行于桂阳。不知其后事果将如何也。学政虽自谓尽心。而只缘已无躬行之实。无以表准多士。使有观感之益。若得如致道令仲和兄诸人。为山长洞主。则诚幸而无奈何矣。此来时。始欲遵仿晦翁南康时事。上闻于 朝。乞赐书籍。且请得山长洞主。而旋思以晦翁而尚被沮格。况今疏贱之踪。何敢为此。遂不免寝罢。而中心则诚有耿耿者矣。台鉴果以道自任。则此诚其责。而亦不敢望其办得矣。前书既以兴起百年之后为教。故今因仰复有此漫及。世人闻之。必大笑矣。亭台两额。刻后当如教印呈。不宣。
与赵子直(辛卯)
即日。伏惟台候动静万福。窃闻有大拜之 命。区区攒喜。曷任鄙诚。向来大病之馀。乃有此举。似尤有不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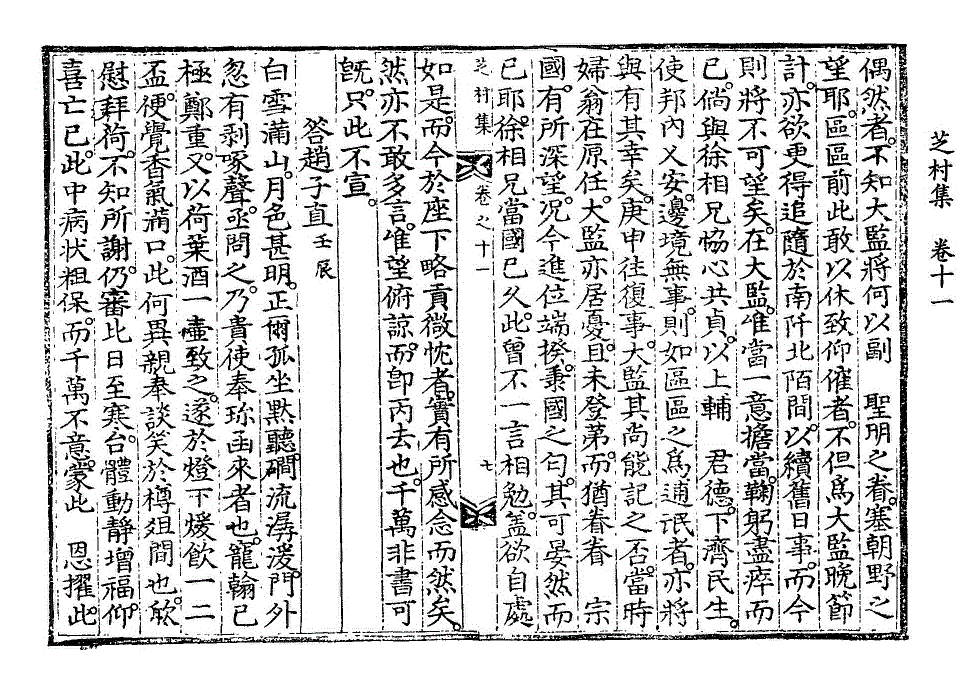 偶然者。不知大监将何以副 圣明之眷。塞朝野之望耶。区区前此敢以休致仰催者。不但为大监晚节计。亦欲更得追随于南阡北陌间。以续旧日事。而今则将不可望矣。在大监。唯当一意担当。鞠躬尽瘁而已。倘与徐相兄协心共贞。以上辅 君德。下济民生。使邦内乂安。边境无事。则如区区之为逋氓者。亦将与有其幸矣。庚申往复事。大监其尚能记之否。当时妇翁在原任。大监亦居忧。且未登第。而犹眷眷 宗国。有所深望。况今进位端揆。秉国之匀。其可晏然而已耶。徐相兄当国已久。此曾不一言相勉。盖欲自处如是。而今于座下略贡微忱者。实有所感念而然矣。然亦不敢多言。唯望俯谅。而即丙去也。千万非书可既。只此不宣。
偶然者。不知大监将何以副 圣明之眷。塞朝野之望耶。区区前此敢以休致仰催者。不但为大监晚节计。亦欲更得追随于南阡北陌间。以续旧日事。而今则将不可望矣。在大监。唯当一意担当。鞠躬尽瘁而已。倘与徐相兄协心共贞。以上辅 君德。下济民生。使邦内乂安。边境无事。则如区区之为逋氓者。亦将与有其幸矣。庚申往复事。大监其尚能记之否。当时妇翁在原任。大监亦居忧。且未登第。而犹眷眷 宗国。有所深望。况今进位端揆。秉国之匀。其可晏然而已耶。徐相兄当国已久。此曾不一言相勉。盖欲自处如是。而今于座下略贡微忱者。实有所感念而然矣。然亦不敢多言。唯望俯谅。而即丙去也。千万非书可既。只此不宣。答赵子直(壬辰)
白雪满山。月色甚明。正尔孤坐默听。涧流潺湲。门外忽有剥啄声。亟问之。乃贵使奉珍函来者也。宠翰已极郑重。又以荷叶酒一壶致之。遂于灯下煖饮一二杯。便觉香气满口。此何异亲奉谈笑于樽俎间也。欣慰拜荷。不知所谢。仍审比日至寒。台体动静增福。仰喜亡已。此中病状粗保。而千万不意。蒙此 恩擢。此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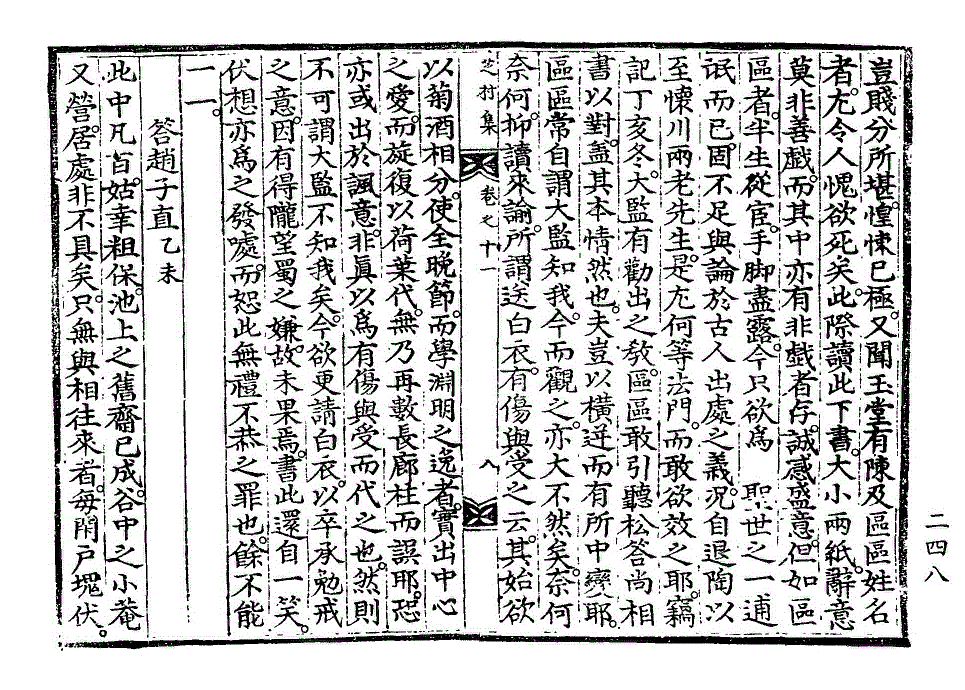 岂贱分所堪。惶悚已极。又闻玉堂有陈及区区姓名者。尤令人愧欲死矣。此际读此下书。大小两纸。辞意莫非善戏。而其中亦有非戏者存。诚感盛意。但如区区者。半生从宦。手脚尽露。今只欲为 圣世之一逋氓而已。固不足与论于古人出处之义。况自退陶以至怀川两老先生。是尤何等法门。而敢欲效之耶。窃记丁亥冬。大监有劝出之教。区区敢引听松答尚相书以对。盖其本情然也。夫岂以横逆而有所中变耶。区区常自谓大监知我。今而观之。亦大不然矣。奈何奈何。抑读来谕。所谓送白衣。有伤与受之云。其始欲以菊酒相分。使全晚节。而学渊明之逸者。实出中心之爱。而旋复以荷叶代。无乃再数长廊柱而误耶。恐亦或出于讽意。非真以为有伤与受而代之也。然则不可谓大监不知我矣。今欲更请白衣。以卒承勉戒之意。因有得陇望蜀之嫌。故未果焉。书此还自一笑。伏想亦为之发噱。而恕此无礼不恭之罪也。馀不能一一。
岂贱分所堪。惶悚已极。又闻玉堂有陈及区区姓名者。尤令人愧欲死矣。此际读此下书。大小两纸。辞意莫非善戏。而其中亦有非戏者存。诚感盛意。但如区区者。半生从宦。手脚尽露。今只欲为 圣世之一逋氓而已。固不足与论于古人出处之义。况自退陶以至怀川两老先生。是尤何等法门。而敢欲效之耶。窃记丁亥冬。大监有劝出之教。区区敢引听松答尚相书以对。盖其本情然也。夫岂以横逆而有所中变耶。区区常自谓大监知我。今而观之。亦大不然矣。奈何奈何。抑读来谕。所谓送白衣。有伤与受之云。其始欲以菊酒相分。使全晚节。而学渊明之逸者。实出中心之爱。而旋复以荷叶代。无乃再数长廊柱而误耶。恐亦或出于讽意。非真以为有伤与受而代之也。然则不可谓大监不知我矣。今欲更请白衣。以卒承勉戒之意。因有得陇望蜀之嫌。故未果焉。书此还自一笑。伏想亦为之发噱。而恕此无礼不恭之罪也。馀不能一一。答赵子直(乙未)
此中凡百。姑幸粗保。池上之旧斋已成。谷中之小庵又营。居处非不具矣。只无与相往来者。每闭户块伏。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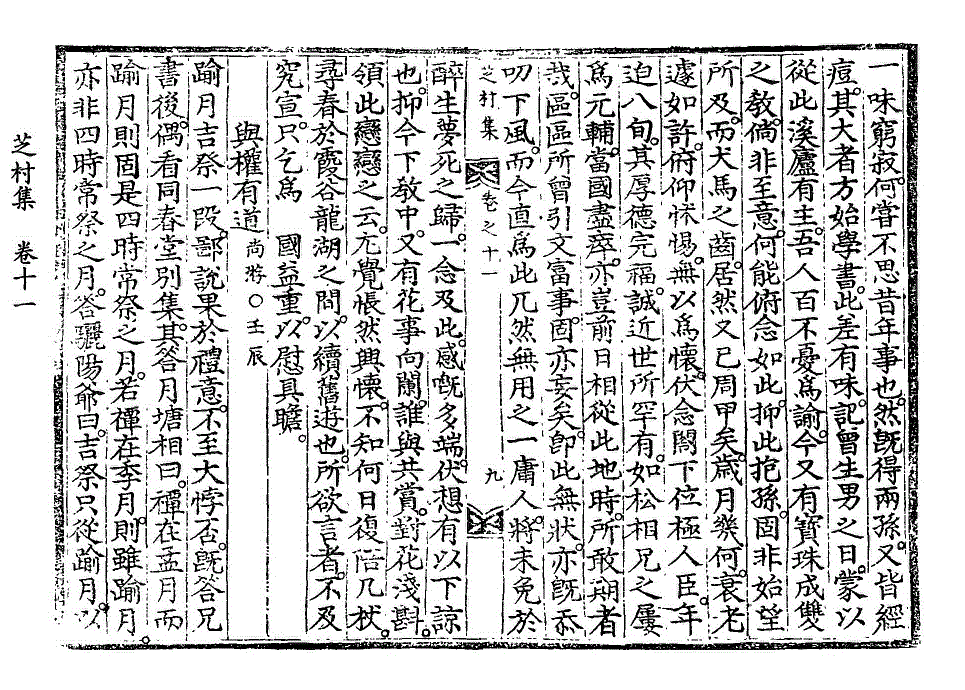 一味穷寂。何尝不思昔年事也。然既得两孙。又皆经痘。其大者方始学书。此差有味。记曾生男之日。蒙以从此溪庐有主。吾人百不忧为谕。今又有宝珠成双之教。倘非至意。何能俯念如此。抑此抱孙。固非始望所及。而犬马之齿。居然又已周甲矣。岁月几何。衰老遽如许。俯仰怵惕。无以为怀。伏念閤下位极人臣。年迫八旬。其厚德完福。诚近世所罕有。如松相兄之屡为元辅。当国尽瘁。亦岂前日相从此地时。所敢期者哉。区区所曾引文富事。固亦妄矣。即此无状。亦既忝叨下风。而今直为此兀然无用之一庸人。将未免于醉生梦死之归。一念及此。感嘅多端。伏想有以下谅也。抑今下教中。又有花事向阑。谁与共赏。对花浅斟。领此恋恋之云。尤觉怅然兴怀。不知何日复陪几杖。寻春于霞谷龙湖之间。以续旧游也。所欲言者。不及究宣。只乞为 国益重。以慰具瞻。
一味穷寂。何尝不思昔年事也。然既得两孙。又皆经痘。其大者方始学书。此差有味。记曾生男之日。蒙以从此溪庐有主。吾人百不忧为谕。今又有宝珠成双之教。倘非至意。何能俯念如此。抑此抱孙。固非始望所及。而犬马之齿。居然又已周甲矣。岁月几何。衰老遽如许。俯仰怵惕。无以为怀。伏念閤下位极人臣。年迫八旬。其厚德完福。诚近世所罕有。如松相兄之屡为元辅。当国尽瘁。亦岂前日相从此地时。所敢期者哉。区区所曾引文富事。固亦妄矣。即此无状。亦既忝叨下风。而今直为此兀然无用之一庸人。将未免于醉生梦死之归。一念及此。感嘅多端。伏想有以下谅也。抑今下教中。又有花事向阑。谁与共赏。对花浅斟。领此恋恋之云。尤觉怅然兴怀。不知何日复陪几杖。寻春于霞谷龙湖之间。以续旧游也。所欲言者。不及究宣。只乞为 国益重。以慰具瞻。与权有道(尚游○壬辰)
踰月吉祭一段。鄙说果于礼意。不至大悖否。既答兄书后。偶看同春堂别集。其答月塘相曰。禫在孟月而踰月则固是四时常祭之月。若禫在季月。则虽踰月。亦非四时常祭之月。答骊阳爷曰。吉祭只从踰月。以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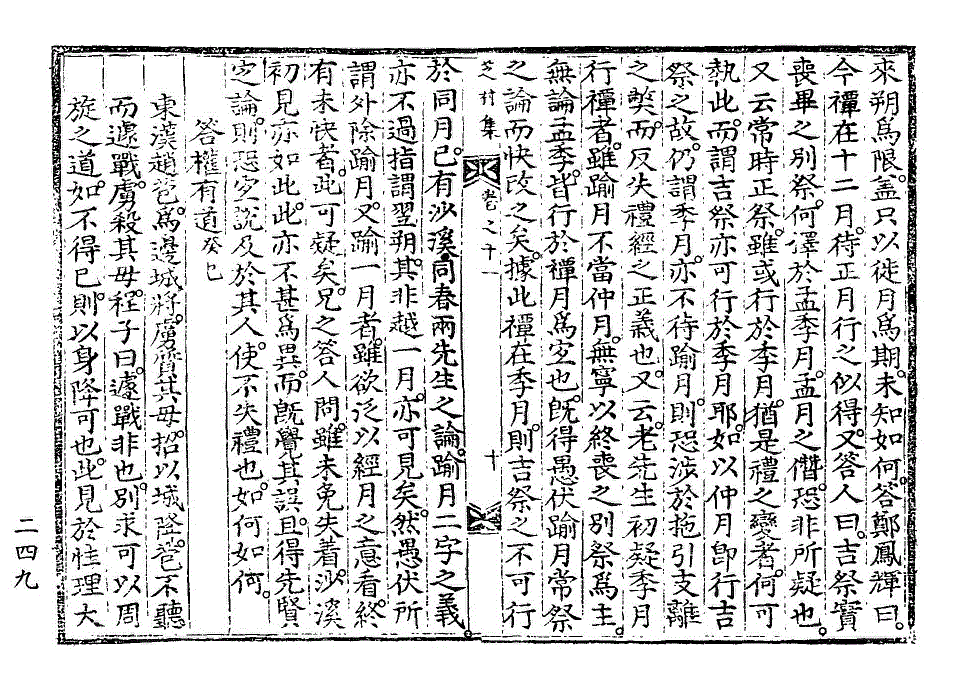 来朔为限。盖只以徙月为期。未知如何。答郑凤辉曰。今禫在十二月。待正月行之似得。又答人曰。吉祭实丧毕之别祭。何择于孟季月。孟月之僭。恐非所疑也。又云常时正祭。虽或行于季月。犹是礼之变者。何可执此。而谓吉祭亦可行于季月耶。如以仲月即行吉祭之故。仍谓季月。亦不待踰月。则恐涉于拖引支离之弊。而反失礼经之正义也。又云。老先生初疑季月行禫者。虽踰月不当仲月。无宁以终丧之别祭为主。无论孟季。皆行于禫月为宜也。既得愚伏踰月常祭之论而快改之矣。据此禫在季月。则吉祭之不可行于同月。已有沙溪,同春两先生之论。踰月二字之义。亦不过指谓翌朔。其非越一月。亦可见矣。然愚伏所谓外除踰月。又踰一月者。虽欲泛以经月之意看。终有未快者。此可疑矣。兄之答人问。虽未免失着。沙溪初见亦如此。此亦不甚为异。而既觉其误。且得先贤定论。则恐宜说及于其人。使不失礼也。如何如何。
来朔为限。盖只以徙月为期。未知如何。答郑凤辉曰。今禫在十二月。待正月行之似得。又答人曰。吉祭实丧毕之别祭。何择于孟季月。孟月之僭。恐非所疑也。又云常时正祭。虽或行于季月。犹是礼之变者。何可执此。而谓吉祭亦可行于季月耶。如以仲月即行吉祭之故。仍谓季月。亦不待踰月。则恐涉于拖引支离之弊。而反失礼经之正义也。又云。老先生初疑季月行禫者。虽踰月不当仲月。无宁以终丧之别祭为主。无论孟季。皆行于禫月为宜也。既得愚伏踰月常祭之论而快改之矣。据此禫在季月。则吉祭之不可行于同月。已有沙溪,同春两先生之论。踰月二字之义。亦不过指谓翌朔。其非越一月。亦可见矣。然愚伏所谓外除踰月。又踰一月者。虽欲泛以经月之意看。终有未快者。此可疑矣。兄之答人问。虽未免失着。沙溪初见亦如此。此亦不甚为异。而既觉其误。且得先贤定论。则恐宜说及于其人。使不失礼也。如何如何。答权有道(癸巳)
东汉赵苞。为边城将。虏质其母。招以城降。苞不听而遽战。虏杀其母。程子曰。遽战非也。别求可以周旋之道。如不得已。则以身降可也。此见于性理大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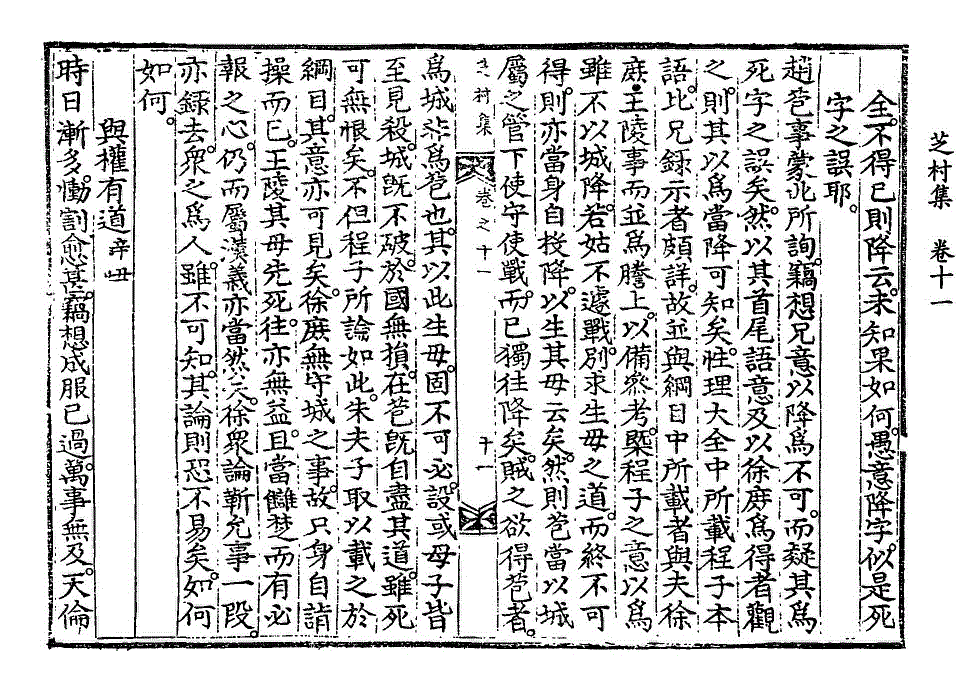 全。不得已则降云。未知果如何。愚意降字。似是死字之误耶。
全。不得已则降云。未知果如何。愚意降字。似是死字之误耶。赵苞事蒙此所询。窃想兄意以降为不可。而疑其为死字之误矣。然以其首尾语意及以徐庶为得者观之。则其以为当降可知矣。性理大全中所载程子本语。比兄录示者颇详。故并与纲目中所载者与夫徐庶,王陵事而并为誊上。以备参考。槩程子之意以为虽不以城降。若姑不遽战。别求生母之道。而终不可得。则亦当身自投降。以生其母云矣。然则苞当以城属之管下使守使战。而已独往降矣。贼之欲得苞者。为城非为苞也。其以此生母。固不可必。设或母子皆至见杀。城既不破。于国无损。在苞既自尽其道。虽死可无恨矣。不但程子所论如此。朱夫子取以载之于纲目。其意亦可见矣。徐庶无守城之事。故只身自诣操而已。王陵其母先死。往亦无益。且当雠楚而有必报之心。仍而属汉义亦当然矣。徐众论靳允事一段。亦录去。众之为人。虽不可知。其论则恐不易矣。如何如何。
与权有道(辛丑)
时日渐多。恸割愈甚。窃想成服已过。万事无及。天伦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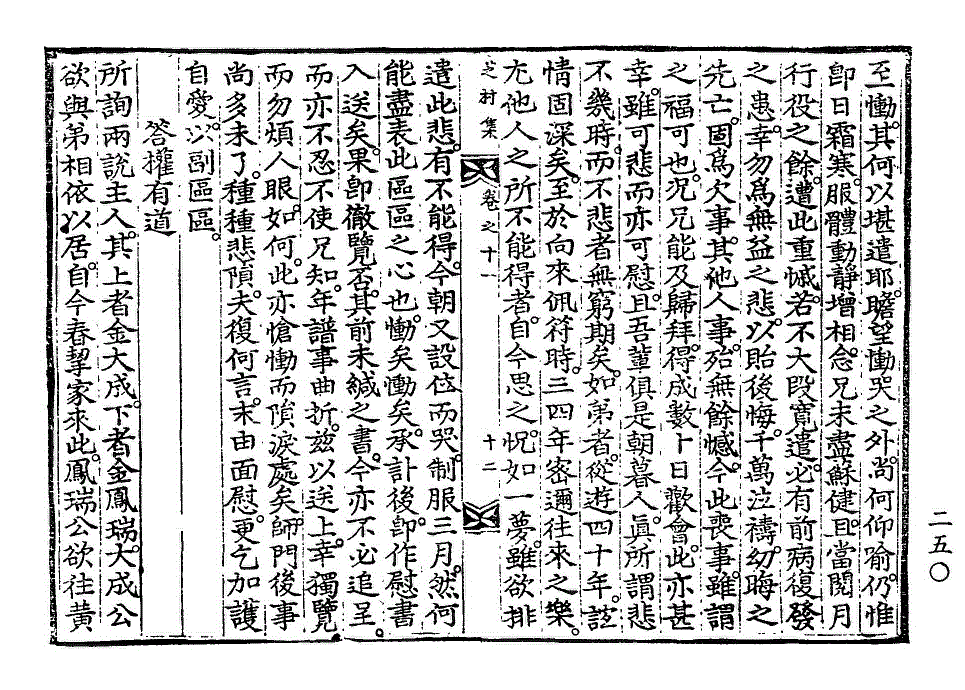 至恸。其何以堪遣耶。瞻望恸哭之外。尚何仰喻。仍惟即日霜寒。服体动静增相。念兄未尽苏健。且当阅月行役之馀。遭此重戚。若不大段宽遣。必有前病复发之患。幸勿为无益之悲。以贻后悔。千万泣祷。幼晦之先亡。固为欠事。其他人事。殆无馀憾。今此丧事。虽谓之福可也。况兄能及归拜。得成数十日欢会。此亦甚幸。虽可悲而亦可慰。且吾辈俱是朝暮人。真所谓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如弟者。从游四十年。谊情固深矣。至于向来佩符时。三四年密迩往来之乐。尤他人之所不能得者。自今思之。恍如一梦。虽欲排遣此悲。有不能得。今朝又设位而哭。制服三月。然何能尽表此区区之心也。恸矣恸矣。承讣后。即作慰书入送矣。果即彻览否。其前未缄之书。今亦不必追呈。而亦不忍不使兄知。年谱事曲折。玆以送上。幸独览而勿烦人眼。如何。此亦怆恸而陨泪处矣。师门后事尚多未了。种种悲陨。夫复何言。末由面慰。更乞加护自爱。以副区区。
至恸。其何以堪遣耶。瞻望恸哭之外。尚何仰喻。仍惟即日霜寒。服体动静增相。念兄未尽苏健。且当阅月行役之馀。遭此重戚。若不大段宽遣。必有前病复发之患。幸勿为无益之悲。以贻后悔。千万泣祷。幼晦之先亡。固为欠事。其他人事。殆无馀憾。今此丧事。虽谓之福可也。况兄能及归拜。得成数十日欢会。此亦甚幸。虽可悲而亦可慰。且吾辈俱是朝暮人。真所谓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如弟者。从游四十年。谊情固深矣。至于向来佩符时。三四年密迩往来之乐。尤他人之所不能得者。自今思之。恍如一梦。虽欲排遣此悲。有不能得。今朝又设位而哭。制服三月。然何能尽表此区区之心也。恸矣恸矣。承讣后。即作慰书入送矣。果即彻览否。其前未缄之书。今亦不必追呈。而亦不忍不使兄知。年谱事曲折。玆以送上。幸独览而勿烦人眼。如何。此亦怆恸而陨泪处矣。师门后事尚多未了。种种悲陨。夫复何言。末由面慰。更乞加护自爱。以副区区。答权有道
所询两说主人。其上者金大成。下者金凤瑞。大成公欲与弟相依以居。自今春挈家来此。凤瑞公欲往黄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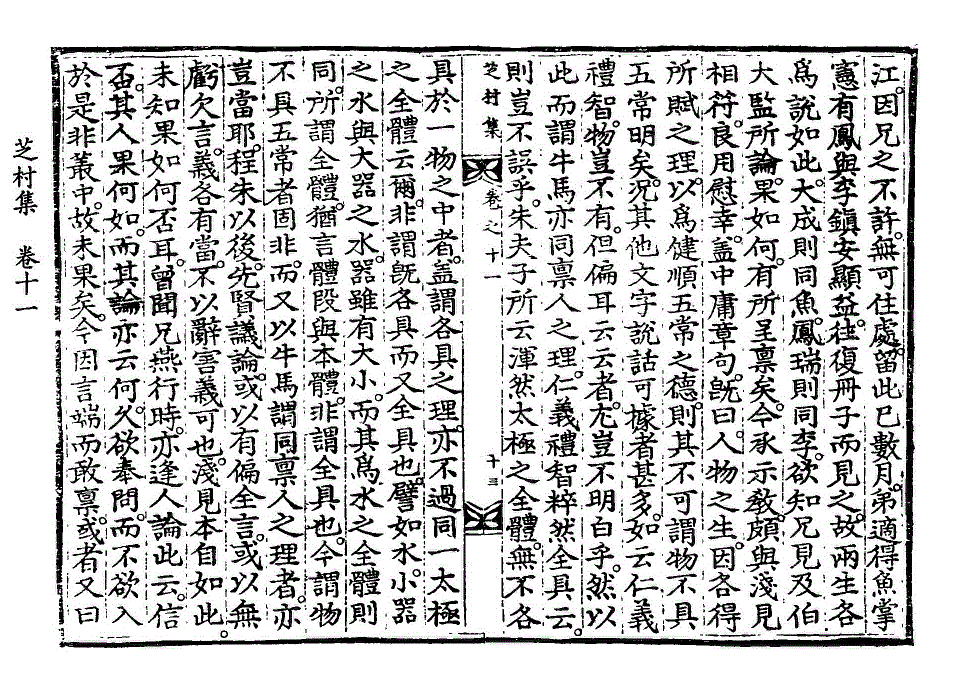 江。因兄之不许。无可住处。留此已数月。弟适得鱼掌宪有凤与李镇安显益。往复册子而见之。故两生各为说如此。大成则同鱼。凤瑞则同李。欲知兄见及伯大监所论。果如何。有所呈禀矣。今承示教。颇与浅见相符。良用慰幸。盖中庸章句。既曰。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则其不可谓物不具五常明矣。况其他文字说话可据者甚多。如云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云云者。尤岂不明白乎。然以此而谓牛马亦同禀人之理。仁义礼智粹然全具云。则岂不误乎。朱夫子所云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者。盖谓各具之理。亦不过同一太极之全体云尔。非谓既各具而又全具也。譬如水。小器之水与大器之水。器虽有大小。而其为水之全体则同。所谓全体。犹言体段与本体。非谓全具也。今谓物不具五常者固非。而又以牛马谓同禀人之理者。亦岂当耶。程朱以后。先贤议论。或以有偏全言。或以无亏欠言。义各有当。不以辞害义可也。浅见本自如此。未知果如何否耳。曾闻兄燕行时。亦逢人论此云。信否。其人果何如。而其论亦云何。久欲奉问。而不欲入于是非丛中。故未果矣。今因言端而敢禀。或者又曰
江。因兄之不许。无可住处。留此已数月。弟适得鱼掌宪有凤与李镇安显益。往复册子而见之。故两生各为说如此。大成则同鱼。凤瑞则同李。欲知兄见及伯大监所论。果如何。有所呈禀矣。今承示教。颇与浅见相符。良用慰幸。盖中庸章句。既曰。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则其不可谓物不具五常明矣。况其他文字说话可据者甚多。如云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云云者。尤岂不明白乎。然以此而谓牛马亦同禀人之理。仁义礼智粹然全具云。则岂不误乎。朱夫子所云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者。盖谓各具之理。亦不过同一太极之全体云尔。非谓既各具而又全具也。譬如水。小器之水与大器之水。器虽有大小。而其为水之全体则同。所谓全体。犹言体段与本体。非谓全具也。今谓物不具五常者固非。而又以牛马谓同禀人之理者。亦岂当耶。程朱以后。先贤议论。或以有偏全言。或以无亏欠言。义各有当。不以辞害义可也。浅见本自如此。未知果如何否耳。曾闻兄燕行时。亦逢人论此云。信否。其人果何如。而其论亦云何。久欲奉问。而不欲入于是非丛中。故未果矣。今因言端而敢禀。或者又曰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1L 页
 所谓偏者。从发处而言。非谓合下不具也。此说未知如何。亦望示及。
所谓偏者。从发处而言。非谓合下不具也。此说未知如何。亦望示及。答申翼仲(镡○庚寅)
近日往复诚可笑。而兄既发端。虽不肯毕其说。弟亦何可全无所对耶。盖兄初书以为直兄谓弟不为为世道计。与古之儒贤规模不同。兄亦以其言为是。故弟敢对以儒贤之称。固非弟所敢当。而然欲闻佥兄所欲使弟自处之如何。则后书所教。又不啻缕缕矣。盖其所传直兄之言。有曰。两大臣与静能是一家。若能左右通议。如美村,玄石之于尤翁。栗谷,牛溪之于思庵。则岂无一分可救之道。而有若高飞长往。果于忘世之为。此甚可惜。兄亦以为寒岗,沙溪官卑之时。亦尝有通议朝论之事。而某友专以退让为务。故弟亦微示警意而不欲变。无可奈何云。而且曰。老兄真有意于斯世。则敢不以所受于古人之徽言。当日之急务。一一条陈云。此其所以期望者。诚不着题。然欲悉闻而有所商量。则兄又谓弟不欲当。而更不开示。诚未知盛意之所在也。盖弟固有自定于中者。然其所谓古人之徽言。当世之急务。果能有闻。而当于心者。则亦岂不有所回禀而求教耶。直兄所谓昔之儒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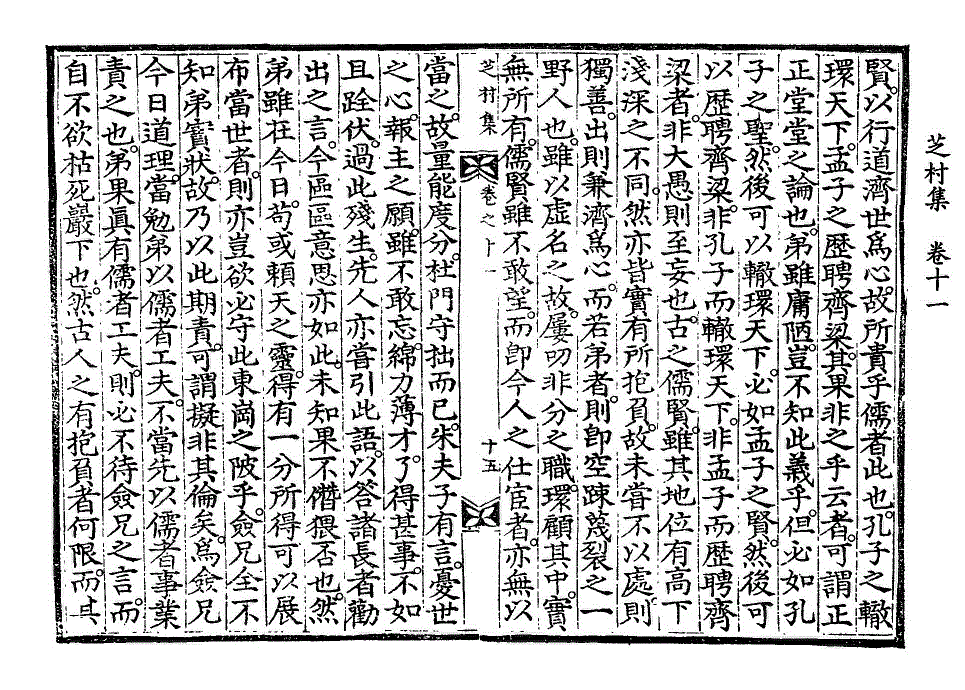 贤。以行道济世为心。故所贵乎儒者此也。孔子之辙环天下。孟子之历聘齐梁。其果非之乎云者。可谓正正堂堂之论也。弟虽庸陋。岂不知此义乎。但必如孔子之圣。然后可以辙环天下。必如孟子之贤。然后可以历聘齐梁。非孔子而辙环天下。非孟子而历聘齐梁者。非大愚则至妄也。古之儒贤。虽其地位有高下浅深之不同。然亦皆实有所抱负。故未尝不以处。则独善。出则兼济为心。而若弟者。则即空疏蔑裂之一野人也。虽以虚名之故。屡叨非分之职。环顾其中。实无所有。儒贤虽不敢望。而即今人之仕宦者。亦无以当之。故量能度分。杜门守拙而已。朱夫子有言。忧世之心。报主之愿。虽不敢忘。绵力薄才。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过此残生。先人亦尝引此语。以答诸长者劝出之言。今区区意思亦如此。未知果不僭猥否也。然弟虽在今日。苟或赖天之灵。得有一分所得可以展布当世者。则亦岂欲必守此东岗之陂乎。佥兄全不知弟实状。故乃以此期责。可谓拟非其伦矣。为佥兄今日道理。当勉弟以儒者工夫。不当先以儒者事业责之也。弟果真有儒者工夫。则必不待佥兄之言。而自不欲枯死岩下也。然古人之有抱负者何限。而其
贤。以行道济世为心。故所贵乎儒者此也。孔子之辙环天下。孟子之历聘齐梁。其果非之乎云者。可谓正正堂堂之论也。弟虽庸陋。岂不知此义乎。但必如孔子之圣。然后可以辙环天下。必如孟子之贤。然后可以历聘齐梁。非孔子而辙环天下。非孟子而历聘齐梁者。非大愚则至妄也。古之儒贤。虽其地位有高下浅深之不同。然亦皆实有所抱负。故未尝不以处。则独善。出则兼济为心。而若弟者。则即空疏蔑裂之一野人也。虽以虚名之故。屡叨非分之职。环顾其中。实无所有。儒贤虽不敢望。而即今人之仕宦者。亦无以当之。故量能度分。杜门守拙而已。朱夫子有言。忧世之心。报主之愿。虽不敢忘。绵力薄才。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过此残生。先人亦尝引此语。以答诸长者劝出之言。今区区意思亦如此。未知果不僭猥否也。然弟虽在今日。苟或赖天之灵。得有一分所得可以展布当世者。则亦岂欲必守此东岗之陂乎。佥兄全不知弟实状。故乃以此期责。可谓拟非其伦矣。为佥兄今日道理。当勉弟以儒者工夫。不当先以儒者事业责之也。弟果真有儒者工夫。则必不待佥兄之言。而自不欲枯死岩下也。然古人之有抱负者何限。而其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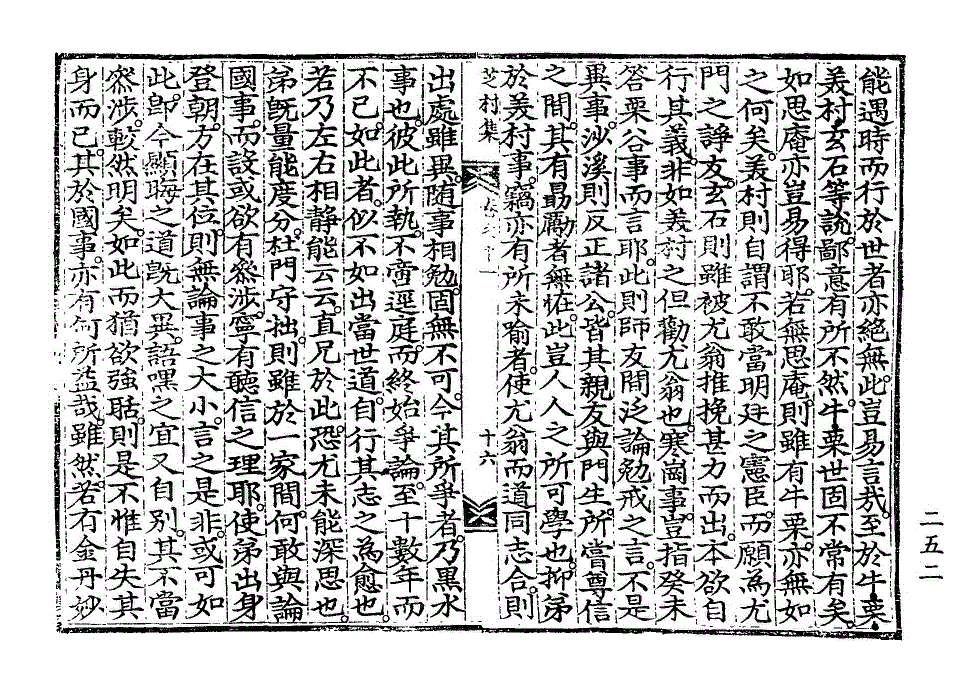 能遇时而行于世者亦绝无。此岂易言哉。至于牛,栗,美村,玄石等说。鄙意有所不然。牛,栗世固不常有矣。如思庵亦岂易得耶。若无思庵。则虽有牛栗。亦无如之何矣。美村则自谓不敢当明廷之宪臣。而愿为尤门之诤友。玄石则虽被尤翁推挽甚力而出。本欲自行其义。非如美村之但劝尤翁也。寒岗事。岂指癸未答栗谷事而言耶。此则师友间泛论勉戒之言。不是异事。沙溪则反正诸公。皆其亲友与门生。所尝尊信之间。其有勖励者无怪。此岂人人之所可学也。抑弟于美村事。窃亦有所未喻者。使尤翁而道同志合。则出处虽异。随事相勉。固无不可。今其所争者。乃黑水事也。彼此所执。不啻径庭。而终始争论。至十数年而不已。如此者。似不如出当世道。自行其志之为愈也。若乃左右相静能云云。直兄于此。恐尤未能深思也。弟既量能度分。杜门守拙。则虽于一家间。何敢与论国事。而设或欲有参涉。宁有听信之理耶。使弟出身登朝。方在其位。则无论事之大小。言之是非。或可如此。即今显晦之道既大异。语嘿之宜又自别。其不当参涉。较然明矣。如此而犹欲强聒。则是不惟自失其身而已。其于国事。亦有何所益哉。虽然。若有金丹妙
能遇时而行于世者亦绝无。此岂易言哉。至于牛,栗,美村,玄石等说。鄙意有所不然。牛,栗世固不常有矣。如思庵亦岂易得耶。若无思庵。则虽有牛栗。亦无如之何矣。美村则自谓不敢当明廷之宪臣。而愿为尤门之诤友。玄石则虽被尤翁推挽甚力而出。本欲自行其义。非如美村之但劝尤翁也。寒岗事。岂指癸未答栗谷事而言耶。此则师友间泛论勉戒之言。不是异事。沙溪则反正诸公。皆其亲友与门生。所尝尊信之间。其有勖励者无怪。此岂人人之所可学也。抑弟于美村事。窃亦有所未喻者。使尤翁而道同志合。则出处虽异。随事相勉。固无不可。今其所争者。乃黑水事也。彼此所执。不啻径庭。而终始争论。至十数年而不已。如此者。似不如出当世道。自行其志之为愈也。若乃左右相静能云云。直兄于此。恐尤未能深思也。弟既量能度分。杜门守拙。则虽于一家间。何敢与论国事。而设或欲有参涉。宁有听信之理耶。使弟出身登朝。方在其位。则无论事之大小。言之是非。或可如此。即今显晦之道既大异。语嘿之宜又自别。其不当参涉。较然明矣。如此而犹欲强聒。则是不惟自失其身而已。其于国事。亦有何所益哉。虽然。若有金丹妙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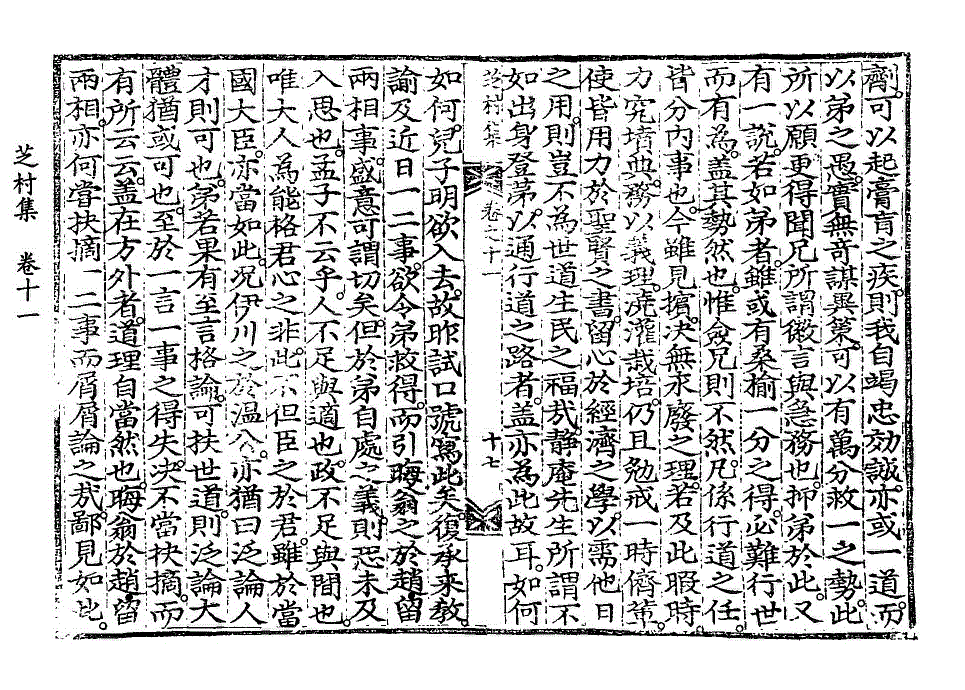 剂。可以起膏肓之疾。则我自竭忠效诚。亦或一道。而以弟之愚。实无奇谋异策。可以有万分救一之势。此所以愿更得闻兄所谓徽言与急务也。抑弟于此。又有一说。若如弟者。虽或有桑榆一分之得。必难行世而有为。盖其势然也。惟佥兄则不然。凡系行道之任。皆分内事也。今虽见摈。决无永废之理。若及此暇时。力究坟典。务以义理。浇灌栽培。仍且勉戒一时侪辈。使皆用力于圣贤之书。留心于经济之学。以需他日之用。则岂不为世道生民之福哉。静庵先生所谓不如出身登第。以通行道之路者。盖亦为此故耳。如何如何。儿子明欲入去。故昨试口号写此矣。复承来教。谕及近日一二事。欲令弟救得。而引晦翁之于赵,留两相事。盛意可谓切矣。但于弟自处之义。则恐未及入思也。孟子不云乎。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此不但臣之于君。虽于当国大臣。亦当如此。况伊川之于温公。亦犹曰泛论人才则可也。弟若果有至言格论。可扶世道。则泛论大体犹或可也。至于一言一事之得失。决不当抉摘。而有所云云。盖在方外者。道理自当然也。晦翁于赵,留两相。亦何尝抉摘一二事而屑屑论之哉。鄙见如此。
剂。可以起膏肓之疾。则我自竭忠效诚。亦或一道。而以弟之愚。实无奇谋异策。可以有万分救一之势。此所以愿更得闻兄所谓徽言与急务也。抑弟于此。又有一说。若如弟者。虽或有桑榆一分之得。必难行世而有为。盖其势然也。惟佥兄则不然。凡系行道之任。皆分内事也。今虽见摈。决无永废之理。若及此暇时。力究坟典。务以义理。浇灌栽培。仍且勉戒一时侪辈。使皆用力于圣贤之书。留心于经济之学。以需他日之用。则岂不为世道生民之福哉。静庵先生所谓不如出身登第。以通行道之路者。盖亦为此故耳。如何如何。儿子明欲入去。故昨试口号写此矣。复承来教。谕及近日一二事。欲令弟救得。而引晦翁之于赵,留两相事。盛意可谓切矣。但于弟自处之义。则恐未及入思也。孟子不云乎。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此不但臣之于君。虽于当国大臣。亦当如此。况伊川之于温公。亦犹曰泛论人才则可也。弟若果有至言格论。可扶世道。则泛论大体犹或可也。至于一言一事之得失。决不当抉摘。而有所云云。盖在方外者。道理自当然也。晦翁于赵,留两相。亦何尝抉摘一二事而屑屑论之哉。鄙见如此。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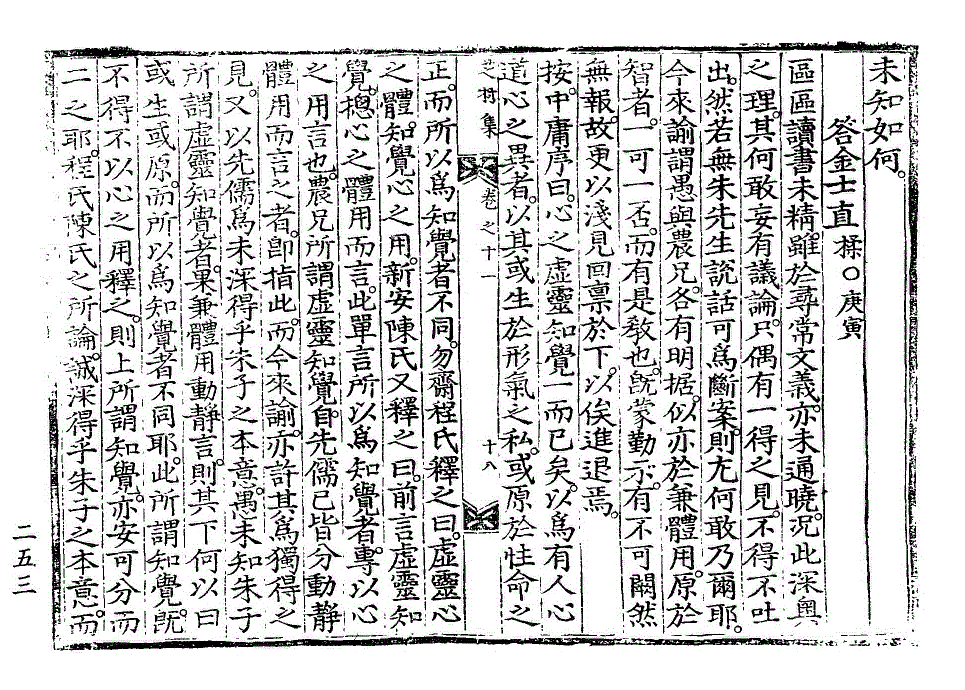 未知如何。
未知如何。答金士直(楺○庚寅)
区区读书未精。虽于寻常文义。亦未通晓。况此深奥之理。其何敢妄有议论。只偶有一得之见。不得不吐出。然若无朱先生说话可为断案。则尤何敢乃尔耶。今来谕谓愚与农兄。各有明据。似亦于兼体用。原于智者。一可一否。而有是教也。既蒙勤示。有不可阙然无报。故更以浅见回禀于下。以俟进退焉。
按。中庸序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勿斋程氏释之曰。虚灵心之体。知觉心之用。新安陈氏又释之曰。前言虚灵知觉。总心之体用而言。此单言所以为知觉者。专以心之用言也。农兄所谓虚灵知觉。自先儒已皆分动静体用而言之者。即指此。而今来谕。亦许其为独得之见。又以先儒为未深得乎朱子之本意。愚未知朱子所谓虚灵知觉者。果兼体用动静言。则其下何以曰或生或原。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耶。此所谓知觉。既不得不以心之用释之。则上所谓知觉。亦安可分而二之耶。程氏陈氏之所论。诚深得乎朱子之本意。而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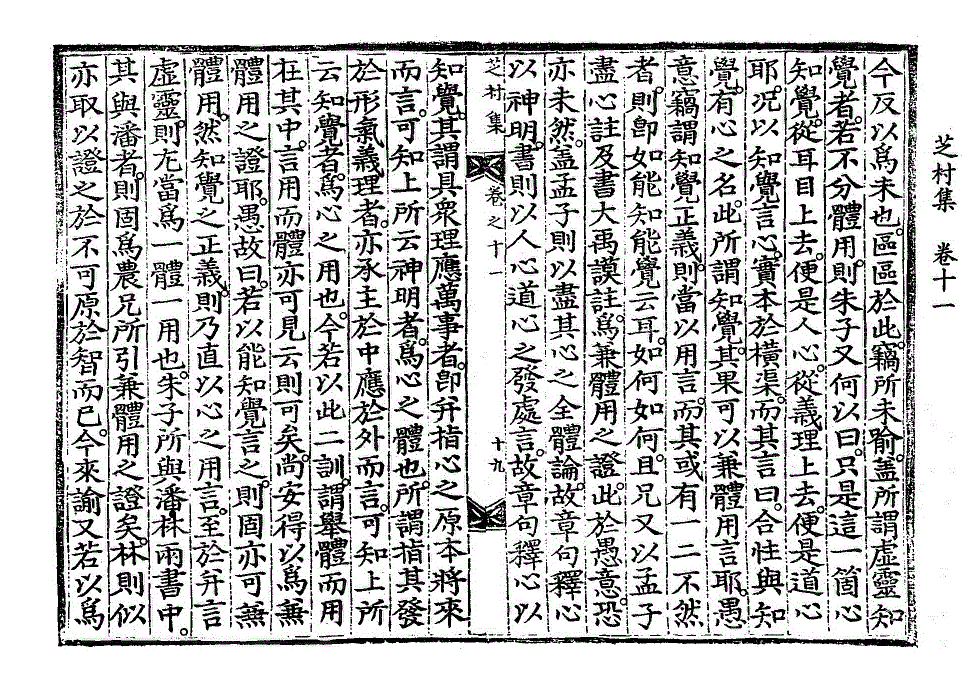 今反以为未也。区区于此。窃所未喻。盖所谓虚灵知觉者。若不分体用。则朱子又何以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上去。便是人心。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耶。况以知觉言心。实本于横渠。而其言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所谓知觉。其果可以兼体用言耶。愚意窃谓知觉正义。则当以用言。而其或有一二不然者。则即如能知能觉云耳。如何如何。且兄又以孟子尽心注及书大禹谟注。为兼体用之證。此于愚意。恐亦未然。盖孟子则以尽其心之全体论。故章句释心以神明。书则以人心道心之发处言。故章句释心以知觉。其谓具众理应万事者。即并指心之原本将来而言。可知上所云神明者。为心之体也。所谓指其发于形气义理者。亦承主于中应于外而言。可知上所云知觉者。为心之用也。今若以此二训。谓举体而用在其中。言用而体亦可见云则可矣。尚安得以为兼体用之證耶。愚故曰。若以能知觉言之。则固亦可兼体用。然知觉之正义。则乃直以心之用言。至于并言虚灵。则尤当为一体一用也。朱子所与潘,林两书中。其与潘者。则固为农兄所引兼体用之證矣。林则似亦取以證之于不可原于智而已。今来谕又若以为
今反以为未也。区区于此。窃所未喻。盖所谓虚灵知觉者。若不分体用。则朱子又何以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上去。便是人心。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耶。况以知觉言心。实本于横渠。而其言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所谓知觉。其果可以兼体用言耶。愚意窃谓知觉正义。则当以用言。而其或有一二不然者。则即如能知能觉云耳。如何如何。且兄又以孟子尽心注及书大禹谟注。为兼体用之證。此于愚意。恐亦未然。盖孟子则以尽其心之全体论。故章句释心以神明。书则以人心道心之发处言。故章句释心以知觉。其谓具众理应万事者。即并指心之原本将来而言。可知上所云神明者。为心之体也。所谓指其发于形气义理者。亦承主于中应于外而言。可知上所云知觉者。为心之用也。今若以此二训。谓举体而用在其中。言用而体亦可见云则可矣。尚安得以为兼体用之證耶。愚故曰。若以能知觉言之。则固亦可兼体用。然知觉之正义。则乃直以心之用言。至于并言虚灵。则尤当为一体一用也。朱子所与潘,林两书中。其与潘者。则固为农兄所引兼体用之證矣。林则似亦取以證之于不可原于智而已。今来谕又若以为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4L 页
 并證于兼体用者然。此则恐或未及深察也。且农兄以大学章句虚灵不昧。为兼体用。此则如来谕所引神明之云矣。至以中庸序虚灵知觉。释之以虚灵而能知觉。虚灵底知觉。此又未知于文义通乎不通乎。夫本文既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上既有之字。则安可复释虚灵知觉曰虚灵而能知觉。虚灵底知觉耶。农兄之见宜不如此。而乃如此。诚未可知也。况其以虚灵为可言于用。而灵又不止于静一边者。亦有可疑。程子所谓心兮本虚。应物无迹者。盖谓心体本虚。故虽应物。而未有痕迹可摸捉。惟于视操之为紧要云尔。夫岂以其用之所行者为虚耶。若灵字则栗谷尝以为心之知处。虽未感物。灵固自若云。据此亦不害为静一边。其安得直以动言之耶。幸于此深思焉。
并證于兼体用者然。此则恐或未及深察也。且农兄以大学章句虚灵不昧。为兼体用。此则如来谕所引神明之云矣。至以中庸序虚灵知觉。释之以虚灵而能知觉。虚灵底知觉。此又未知于文义通乎不通乎。夫本文既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上既有之字。则安可复释虚灵知觉曰虚灵而能知觉。虚灵底知觉耶。农兄之见宜不如此。而乃如此。诚未可知也。况其以虚灵为可言于用。而灵又不止于静一边者。亦有可疑。程子所谓心兮本虚。应物无迹者。盖谓心体本虚。故虽应物。而未有痕迹可摸捉。惟于视操之为紧要云尔。夫岂以其用之所行者为虚耶。若灵字则栗谷尝以为心之知处。虽未感物。灵固自若云。据此亦不害为静一边。其安得直以动言之耶。幸于此深思焉。按。心即所能知觉者。故固有以知觉。谓之心者。然恐不可谓心之体段。盖体段之云。犹可言于虚灵。而不可言于知觉也。且谓气安有兼体用之气乎。而又以所知觉谓主乎中。能知觉谓应乎外。此亦未安。体用二字就气上。亦可分动静言之。安得谓之气不兼体用乎。若所谓主乎中应乎外者。盖指心而言曰。主一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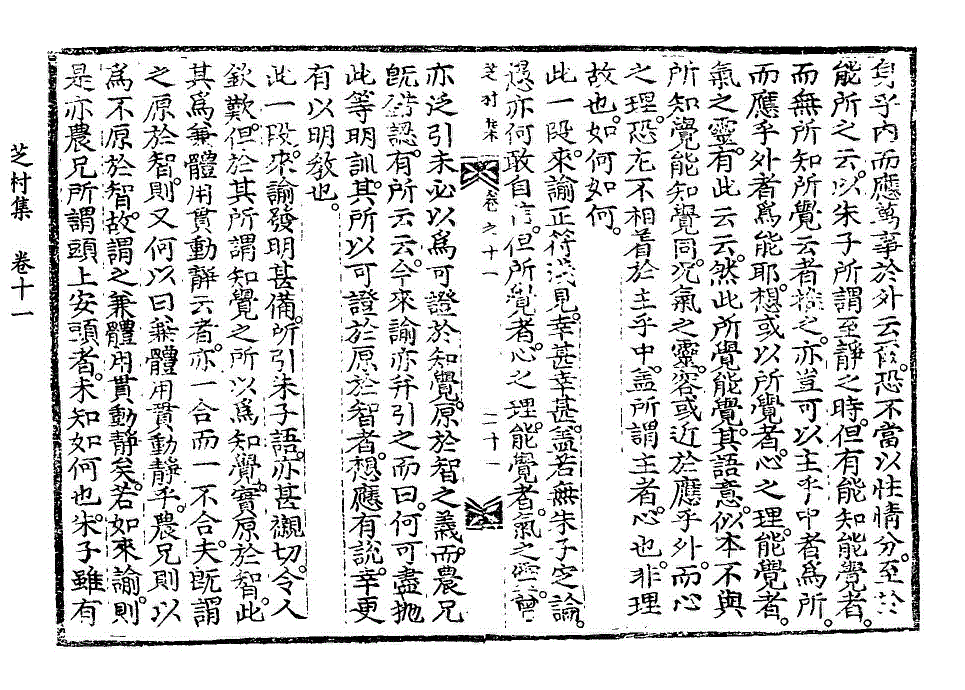 身乎内而应万事于外云尔。恐不当以性情分。至于能所之云。以朱子所谓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无所知所觉云者推之。亦岂可以主乎中者为所。而应乎外者为能耶。想或以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有此云云。然此所觉能觉。其语意。似本不与所知觉能知觉同。况气之灵。容或近于应乎外。而心之理。恐尤不相着于主乎中。盖所谓主者。心也。非理故也。如何如何。
身乎内而应万事于外云尔。恐不当以性情分。至于能所之云。以朱子所谓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无所知所觉云者推之。亦岂可以主乎中者为所。而应乎外者为能耶。想或以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有此云云。然此所觉能觉。其语意。似本不与所知觉能知觉同。况气之灵。容或近于应乎外。而心之理。恐尤不相着于主乎中。盖所谓主者。心也。非理故也。如何如何。此一段。来谕正符浅见。幸甚幸甚。盖若无朱子定论。愚亦何敢自信。但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曾亦泛引未必以为可證于知觉。原于智之义。而农兄既错认。有所云云。今来谕亦并引之而曰。何可尽抛此等明训。其所以可證于原于智者。想应有说。幸更有以明教也。
此一段。来谕发明甚备。所引朱子语。亦甚衬切。令人钦叹。但于其所谓知觉之所以为知觉。实原于智。此其为兼体用贯动静云者。亦一合而一不合。夫既谓之原于智。则又何以曰兼体用贯动静乎。农兄则以为不原于智。故谓之兼体用贯动静矣。若如来谕。则是亦农兄所谓头上安头者。未知如何也。朱子虽有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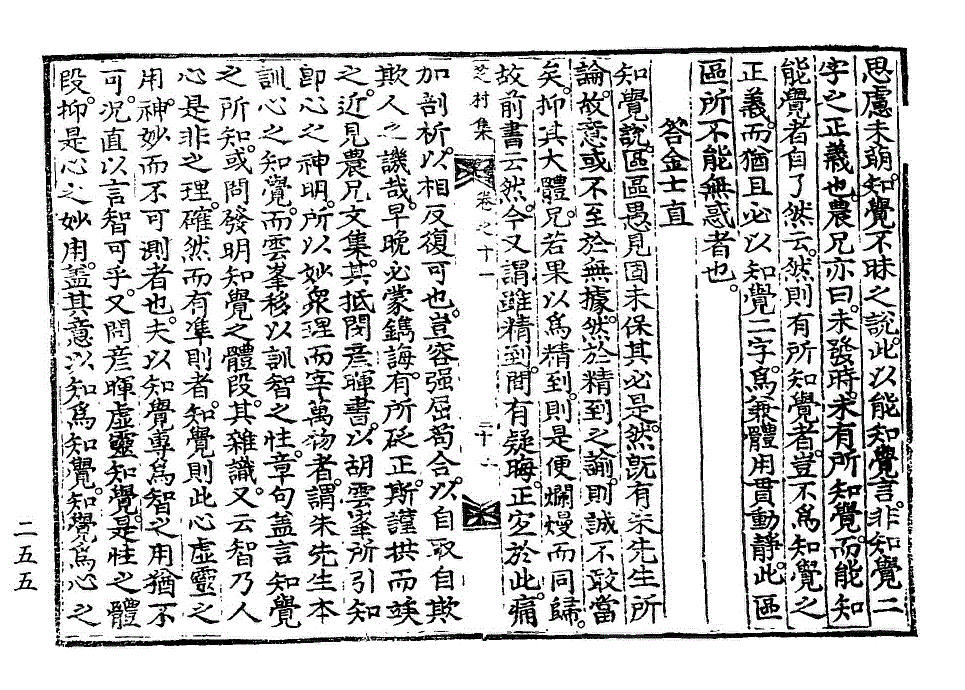 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之说。此以能知觉言。非知觉二字之正义也。农兄亦曰。未发时。未有所知觉。而能知能觉者自了然云。然则有所知觉者。岂不为知觉之正义。而犹且必以知觉二字。为兼体用贯动静。此区区所不能无惑者也。
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之说。此以能知觉言。非知觉二字之正义也。农兄亦曰。未发时。未有所知觉。而能知能觉者自了然云。然则有所知觉者。岂不为知觉之正义。而犹且必以知觉二字。为兼体用贯动静。此区区所不能无惑者也。答金士直
知觉说。区区愚见固未保其必是。然既有朱先生所论。故意或不至于无据。然于精到之谕。则诚不敢当矣。抑其大体。兄若果以为精到。则是便烂熳而同归。故前书云然。今又谓虽精到。间有疑晦。正宜于此。痛加剖析。以相反复可也。岂容强屈苟合。以自取自欺欺人之讥哉。早晚必蒙镌诲。有所砭正。斯谨拱而俟之。近见农兄文集。其抵闵彦晖书。以胡云峰所引知即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谓朱先生本训心之知觉。而云峰移以训智之性。章句盖言知觉之所知。或问发明知觉之体段。其杂识。又云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确然而有准则者。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夫以知觉专为智之用犹不可。况直以言智可乎。又问彦晖虚灵知觉。是性之体段。抑是心之妙用。盖其意以知为知觉。知觉为心之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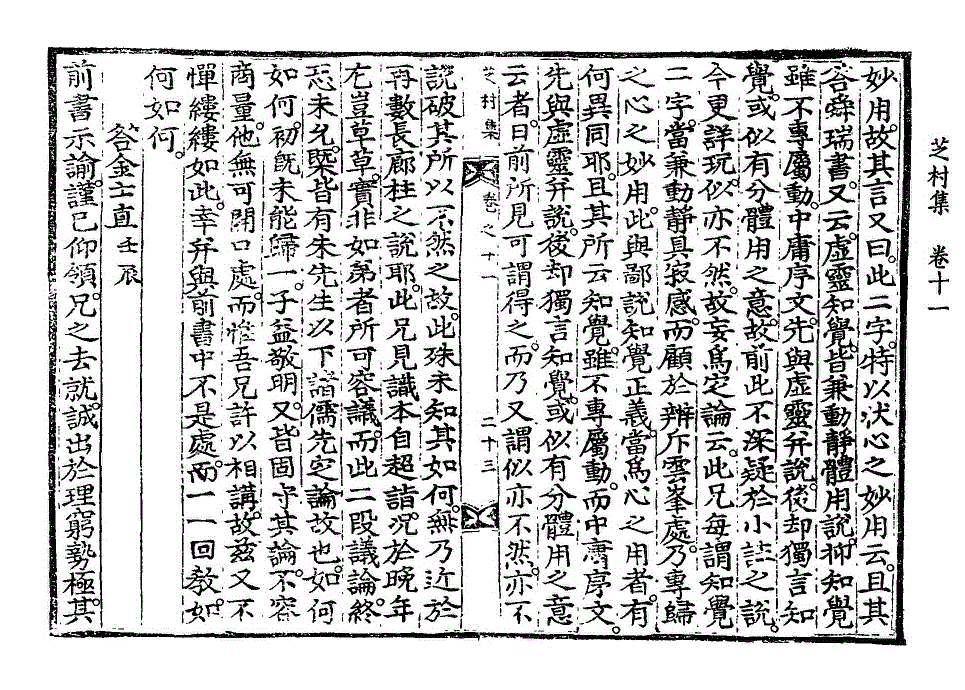 妙用。故其言又曰。此二字。特以状心之妙用云。且其答舜瑞书。又云。虚灵知觉。皆兼动静体用说。抑知觉虽不专属动。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或似有分体用之意。故前此不深疑于小注之说。今更详玩。似亦不然。故妄为定论云。此兄每谓知觉二字。当兼动静具寂感。而顾于辨斥云峰处。乃专归之心之妙用。此与鄙说知觉正义。当为心之用者。有何异同耶。且其所云知觉。虽不专属动。而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或似有分体用之意云者。日前所见可谓得之。而乃又谓似亦不然。亦不说破其所以不然之故。此殊未知其如何。无乃近于再数长廊柱之说耶。此兄见识本自超诣。况于晚年尤岂草草。实非如弟者所可容议。而此二段议论。终恐未允。槩皆有朱先生以下诸儒先定论故也。如何如何。初既未能归一。子益敬明。又皆固守其论。不容商量。他无可开口处。而惟吾兄许以相讲。故玆又不惮缕缕如此。幸并与前书中不是处。而一一回教。如何如何。
妙用。故其言又曰。此二字。特以状心之妙用云。且其答舜瑞书。又云。虚灵知觉。皆兼动静体用说。抑知觉虽不专属动。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或似有分体用之意。故前此不深疑于小注之说。今更详玩。似亦不然。故妄为定论云。此兄每谓知觉二字。当兼动静具寂感。而顾于辨斥云峰处。乃专归之心之妙用。此与鄙说知觉正义。当为心之用者。有何异同耶。且其所云知觉。虽不专属动。而中庸序文。先与虚灵并说。后却独言知觉。或似有分体用之意云者。日前所见可谓得之。而乃又谓似亦不然。亦不说破其所以不然之故。此殊未知其如何。无乃近于再数长廊柱之说耶。此兄见识本自超诣。况于晚年尤岂草草。实非如弟者所可容议。而此二段议论。终恐未允。槩皆有朱先生以下诸儒先定论故也。如何如何。初既未能归一。子益敬明。又皆固守其论。不容商量。他无可开口处。而惟吾兄许以相讲。故玆又不惮缕缕如此。幸并与前书中不是处。而一一回教。如何如何。答金士直(壬辰)
前书示谕。谨已仰领。兄之去就。诚出于理穷势极。其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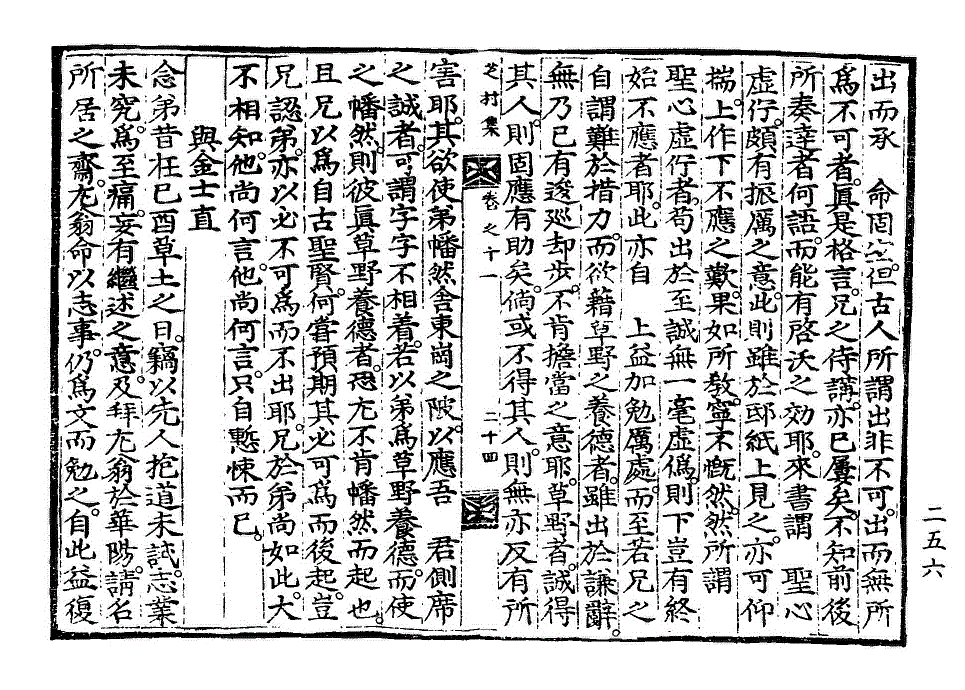 出而承 命固宜。但古人所谓出非不可。出而无所为不可者。真是格言。兄之侍讲。亦已屡矣。不知前后所奏达者何语。而能有启沃之效耶。来书谓 圣心虚伫。颇有振厉之意。此则虽于邸纸上见之。亦可仰揣。上作下不应之叹。果如所教。宁不慨然。然所谓 圣心虚伫者。苟出于至诚无一毫虚伪。则下岂有终始不应者耶。此亦自 上益加勉厉处。而至若兄之自谓难于措力。而欲藉草野之养德者。虽出于谦辞。无乃已有逡巡却步。不肯担当之意耶。草野者。诚得其人。则固应有助矣。倘或不得其人。则无亦(一作益)反有所害耶。其欲使弟幡然舍东岗之陂。以应吾 君侧席之诚者。可谓字字不相着。若以弟为草野养德。而使之幡然。则彼真草野养德者。恐尤不肯幡然而起也。且兄以为自古圣贤。何尝预期其必可为而后起。岂兄认弟。亦以必不可为而不出耶。兄于弟尚如此。大不相知。他尚何言。他尚何言。只自惭悚而已。
出而承 命固宜。但古人所谓出非不可。出而无所为不可者。真是格言。兄之侍讲。亦已屡矣。不知前后所奏达者何语。而能有启沃之效耶。来书谓 圣心虚伫。颇有振厉之意。此则虽于邸纸上见之。亦可仰揣。上作下不应之叹。果如所教。宁不慨然。然所谓 圣心虚伫者。苟出于至诚无一毫虚伪。则下岂有终始不应者耶。此亦自 上益加勉厉处。而至若兄之自谓难于措力。而欲藉草野之养德者。虽出于谦辞。无乃已有逡巡却步。不肯担当之意耶。草野者。诚得其人。则固应有助矣。倘或不得其人。则无亦(一作益)反有所害耶。其欲使弟幡然舍东岗之陂。以应吾 君侧席之诚者。可谓字字不相着。若以弟为草野养德。而使之幡然。则彼真草野养德者。恐尤不肯幡然而起也。且兄以为自古圣贤。何尝预期其必可为而后起。岂兄认弟。亦以必不可为而不出耶。兄于弟尚如此。大不相知。他尚何言。他尚何言。只自惭悚而已。与金士直
念弟昔在己酉草土之日。窃以先人抱道未试。志业未究。为至痛。妄有继述之意。及拜尤翁于华阳。请名所居之斋。尤翁命以志事。仍为文而勉之。自此益复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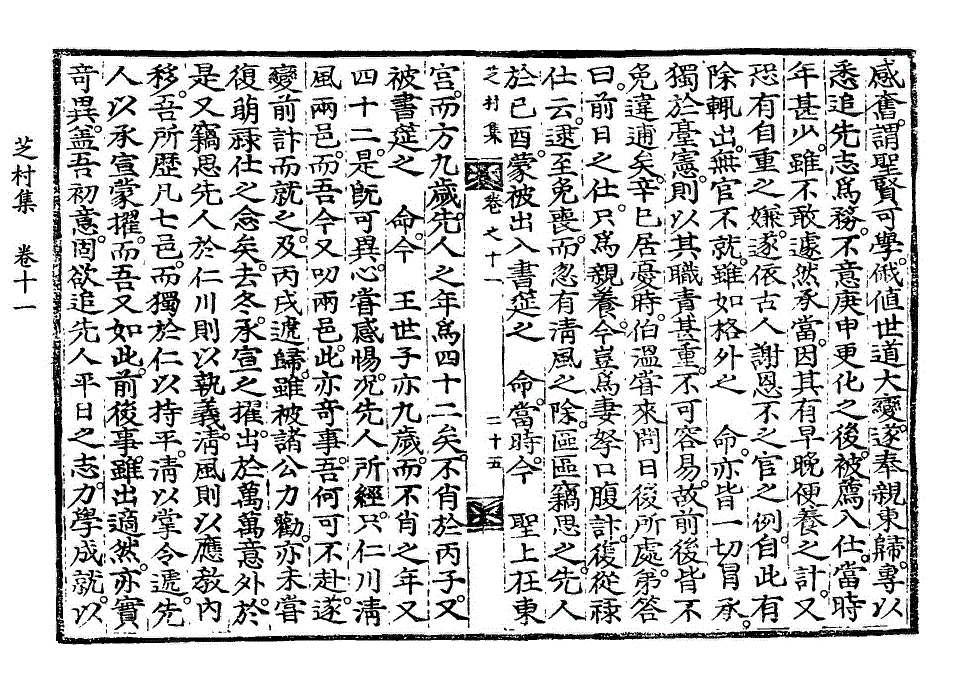 感奋。谓圣贤可学。俄值世道大变。遂奉亲东归。专以悉追先志为务。不意庚申更化之后。被荐入仕。当时年甚少。虽不敢遽然承当。因其有早晚便养之计。又恐有自重之嫌。遂依古人谢恩不之官之例。自此有除辄出。无官不就。虽如格外之 命。亦皆一切冒承。独于台宪。则以其职责甚重。不可容易。故前后皆不免违逋矣。辛巳居忧时。伯温尝来问日后所处。弟答曰。前日之仕。只为亲养。今岂为妻孥口腹计。复从禄仕云。逮至免丧。而忽有清风之除。区区窃思之。先人于己酉。蒙被出入书筵之 命。当时。今 圣上在东宫。而方九岁。先人之年为四十二矣。不肖于丙子。又被书筵之 命。今 王世子亦九岁。而不肖之年又四十二。是既可异。心尝感惕。况先人所经。只仁川清风两邑。而吾今又叨两邑。此亦奇事。吾何可不赴。遂变前计而就之。及丙戌递归。虽被诸公力劝。亦未尝复萌禄仕之念矣。去冬。承宣之擢。出于万万意外。于是又窃思先人于仁川则以执义。清风则以应教内移。吾所历凡七邑。而独于仁以持平。清以掌令递。先人以承宣蒙擢。而吾又如此。前后事。虽出适然。亦实奇异。盖吾初意。固欲追先人平日之志。力学成就。以
感奋。谓圣贤可学。俄值世道大变。遂奉亲东归。专以悉追先志为务。不意庚申更化之后。被荐入仕。当时年甚少。虽不敢遽然承当。因其有早晚便养之计。又恐有自重之嫌。遂依古人谢恩不之官之例。自此有除辄出。无官不就。虽如格外之 命。亦皆一切冒承。独于台宪。则以其职责甚重。不可容易。故前后皆不免违逋矣。辛巳居忧时。伯温尝来问日后所处。弟答曰。前日之仕。只为亲养。今岂为妻孥口腹计。复从禄仕云。逮至免丧。而忽有清风之除。区区窃思之。先人于己酉。蒙被出入书筵之 命。当时。今 圣上在东宫。而方九岁。先人之年为四十二矣。不肖于丙子。又被书筵之 命。今 王世子亦九岁。而不肖之年又四十二。是既可异。心尝感惕。况先人所经。只仁川清风两邑。而吾今又叨两邑。此亦奇事。吾何可不赴。遂变前计而就之。及丙戌递归。虽被诸公力劝。亦未尝复萌禄仕之念矣。去冬。承宣之擢。出于万万意外。于是又窃思先人于仁川则以执义。清风则以应教内移。吾所历凡七邑。而独于仁以持平。清以掌令递。先人以承宣蒙擢。而吾又如此。前后事。虽出适然。亦实奇异。盖吾初意。固欲追先人平日之志。力学成就。以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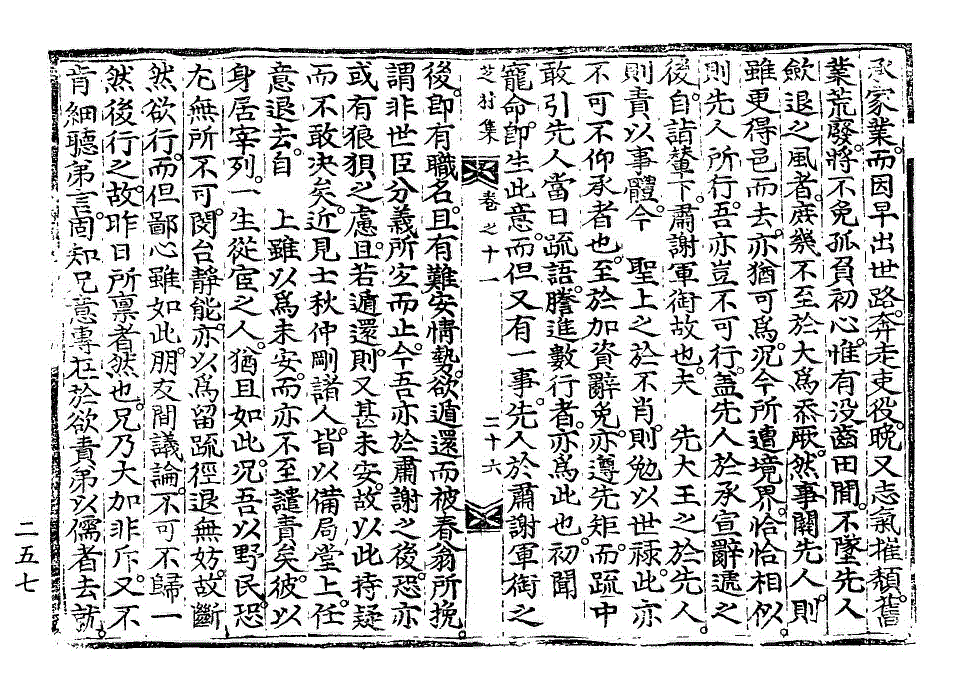 承家业。而因早出世路。奔走吏役。晚又志气摧颓。旧业荒废。将不免孤负初心。惟有没齿田间。不坠先人敛退之风者。庶几不至于大为忝厥。然事关先人。则虽更得邑而去。亦犹可为。况今所遭境界。恰恰相似。则先人所行。吾亦岂不可行。盖先人于承宣辞递之后。自诣辇下。肃谢军衔故也。夫 先大王之于先人。则责以事体。今 圣上之于不肖。则勉以世禄。此亦不可不仰承者也。至于加资辞免。亦遵先矩。而疏中敢引先人当日疏语。誊进数行者。亦为此也。初闻 宠命。即生此意。而但又有一事。先人于肃谢军衔之后。即有职名。且有难安情势。欲遁还而被春翁所挽。谓非世臣分义所宜而止。今吾亦于肃谢之后。恐亦或有狼狈之虑。且若遁还。则又甚未安。故以此持疑而不敢决矣。近见士秋仲刚诸人。皆以备局堂上。任意退去。自 上虽以为未安。而亦不至谴责矣。彼以身居宰列。一生从宦之人。犹且如此。况吾以野民。恐尤无所不可。闵台静能。亦以为留疏径退无妨。故断然欲行。而但鄙心虽如此。朋友间议论。不可不归一然后行之。故昨日所禀者然也。兄乃大加非斥。又不肯细听弟言。固知兄意专在于欲责弟以儒者去就。
承家业。而因早出世路。奔走吏役。晚又志气摧颓。旧业荒废。将不免孤负初心。惟有没齿田间。不坠先人敛退之风者。庶几不至于大为忝厥。然事关先人。则虽更得邑而去。亦犹可为。况今所遭境界。恰恰相似。则先人所行。吾亦岂不可行。盖先人于承宣辞递之后。自诣辇下。肃谢军衔故也。夫 先大王之于先人。则责以事体。今 圣上之于不肖。则勉以世禄。此亦不可不仰承者也。至于加资辞免。亦遵先矩。而疏中敢引先人当日疏语。誊进数行者。亦为此也。初闻 宠命。即生此意。而但又有一事。先人于肃谢军衔之后。即有职名。且有难安情势。欲遁还而被春翁所挽。谓非世臣分义所宜而止。今吾亦于肃谢之后。恐亦或有狼狈之虑。且若遁还。则又甚未安。故以此持疑而不敢决矣。近见士秋仲刚诸人。皆以备局堂上。任意退去。自 上虽以为未安。而亦不至谴责矣。彼以身居宰列。一生从宦之人。犹且如此。况吾以野民。恐尤无所不可。闵台静能。亦以为留疏径退无妨。故断然欲行。而但鄙心虽如此。朋友间议论。不可不归一然后行之。故昨日所禀者然也。兄乃大加非斥。又不肯细听弟言。固知兄意专在于欲责弟以儒者去就。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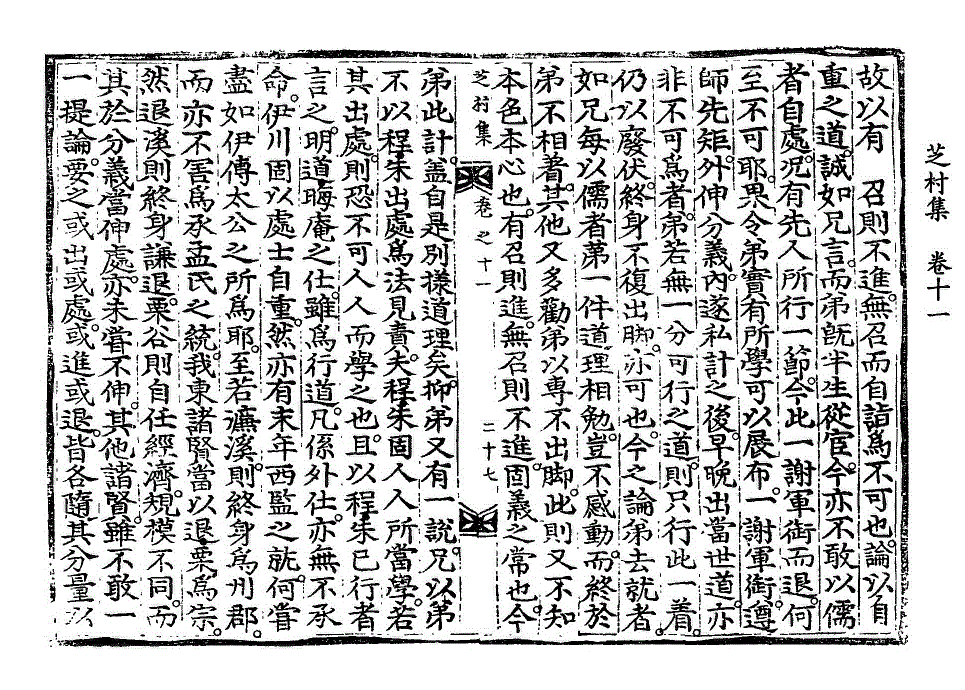 故以有 召则不进。无召而自诣为不可也。论以自重之道。诚如兄言。而弟既半生从宦。今亦不敢以儒者自处。况有先人所行一节。今此一谢军衔而退。何至不可耶。果令弟实有所学可以展布。一谢军衔。遵师先矩。外伸分义。内遂私计之后。早晚出当世道。亦非不可为者。弟若无一分可行之道。则只行此一着。仍以废伏。终身不复出脚。亦可也。今之论弟去就者。如兄每以儒者第一件道理相勉。岂不感动。而终于弟不相着。其他又多劝弟以专不出脚。此则又不知本色本心也。有召则进。无召则不进。固义之常也。今弟此计。盖自是别㨾道理矣。抑弟又有一说。兄以弟不以程,朱出处为法见责。夫程,朱固人人所当学。若其出处。则恐不可人人而学之也。且以程,朱已行者言之。明道,晦庵之仕。虽为行道。凡系外仕。亦无不承命。伊川固以处士自重。然亦有末年西监之就。何尝尽如伊傅太公之所为耶。至若濂溪。则终身为州郡。而亦不害为承孟氏之统。我东诸贤当以退,栗为宗。然退溪则终身谦退。栗谷则自任经济。规模不同。而其于分义当伸处。亦未尝不伸。其他诸贤。虽不敢一一提论。要之或出或处。或进或退。皆各随其分量以
故以有 召则不进。无召而自诣为不可也。论以自重之道。诚如兄言。而弟既半生从宦。今亦不敢以儒者自处。况有先人所行一节。今此一谢军衔而退。何至不可耶。果令弟实有所学可以展布。一谢军衔。遵师先矩。外伸分义。内遂私计之后。早晚出当世道。亦非不可为者。弟若无一分可行之道。则只行此一着。仍以废伏。终身不复出脚。亦可也。今之论弟去就者。如兄每以儒者第一件道理相勉。岂不感动。而终于弟不相着。其他又多劝弟以专不出脚。此则又不知本色本心也。有召则进。无召则不进。固义之常也。今弟此计。盖自是别㨾道理矣。抑弟又有一说。兄以弟不以程,朱出处为法见责。夫程,朱固人人所当学。若其出处。则恐不可人人而学之也。且以程,朱已行者言之。明道,晦庵之仕。虽为行道。凡系外仕。亦无不承命。伊川固以处士自重。然亦有末年西监之就。何尝尽如伊傅太公之所为耶。至若濂溪。则终身为州郡。而亦不害为承孟氏之统。我东诸贤当以退,栗为宗。然退溪则终身谦退。栗谷则自任经济。规模不同。而其于分义当伸处。亦未尝不伸。其他诸贤。虽不敢一一提论。要之或出或处。或进或退。皆各随其分量以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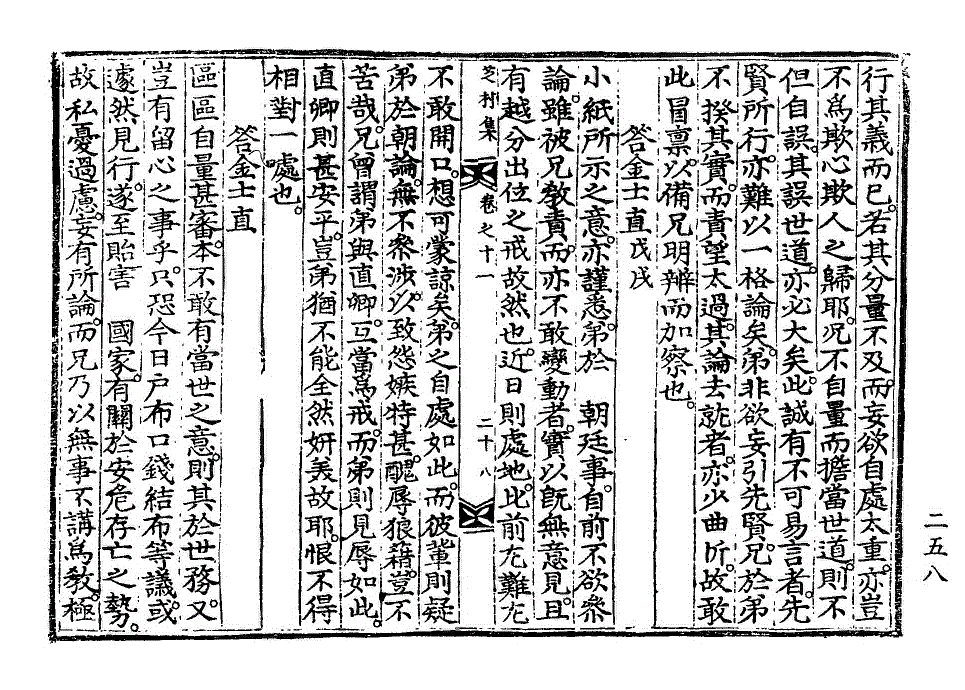 行其义而已。若其分量不及。而妄欲自处太重。亦岂不为欺心欺人之归耶。况不自量而担当世道。则不但自误。其误世道。亦必大矣。此诚有不可易言者。先贤所行。亦难以一格论矣。弟非欲妄引先贤。兄于弟不揆其实。而责望太过。其论去就者。亦少曲折。故敢此冒禀。以备兄明辨而加察也。
行其义而已。若其分量不及。而妄欲自处太重。亦岂不为欺心欺人之归耶。况不自量而担当世道。则不但自误。其误世道。亦必大矣。此诚有不可易言者。先贤所行。亦难以一格论矣。弟非欲妄引先贤。兄于弟不揆其实。而责望太过。其论去就者。亦少曲折。故敢此冒禀。以备兄明辨而加察也。答金士直(戊戌)
小纸所示之意。亦谨悉。弟于 朝廷事。自前不欲参论。虽被兄教责。而亦不敢变动者。实以既无意见。且有越分出位之戒故然也。近日则处地。比前尤难尤不敢开口。想可蒙谅矣。弟之自处如此。而彼辈则疑弟于朝论。无不参涉。以致怨嫉特甚。丑辱狼藉。岂不苦哉。兄曾谓弟与直卿。互当为戒。而弟则见辱如此。直卿则甚安平。岂弟犹不能全然妍美故耶。恨不得相对一噱也。
答金士直
区区自量甚审。本不敢有当世之意。则其于世务。又岂有留心之事乎。只恐今日户布口钱结布等议。或遽然见行。遂至贻害 国家。有关于安危存亡之势。故私忧过虑。妄有所论。而兄乃以无事不讲为教。极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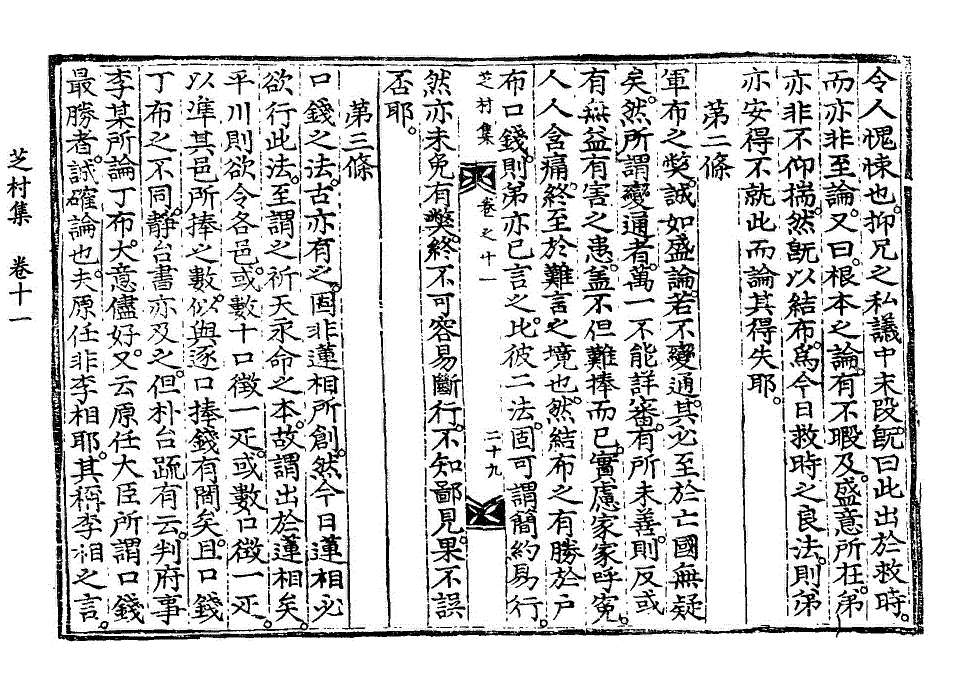 令人愧悚也。抑兄之私议中末段。既曰此出于救时。而亦非至论。又曰。根本之论。有不暇及。盛意所在。弟亦非不仰揣。然既以结布。为今日救时之良法。则弟亦安得不就此而论其得失耶。
令人愧悚也。抑兄之私议中末段。既曰此出于救时。而亦非至论。又曰。根本之论。有不暇及。盛意所在。弟亦非不仰揣。然既以结布。为今日救时之良法。则弟亦安得不就此而论其得失耶。第二条
军布之弊。诚如盛论。若不变通。其必至于亡国无疑矣。然所谓变通者。万一不能详审。有所未善。则反或有无益有害之患。盖不但难捧而已。实虑家家呼冤。人人含痛。终至于难言之境也。然结布之有胜于户布口钱。则弟亦已言之。比彼二法。固可谓简约易行。然亦未免有弊。终不可容易断行。不知鄙见。果不误否耶。
第三条
口钱之法。古亦有之。固非莲相所创。然今日莲相必欲行此法。至谓之祈天永命之本。故谓出于莲相矣。平川则欲令各邑。或数十口徵一疋。或数口徵一疋。以准其邑所捧之数。似与逐口捧钱有间矣。且口钱丁布之不同。静台书亦及之。但朴台疏有云。判府事李某所论丁布。大意尽好。又云原任大臣所谓口钱最胜者。诚确论也。夫原任非李相耶。其称李相之言。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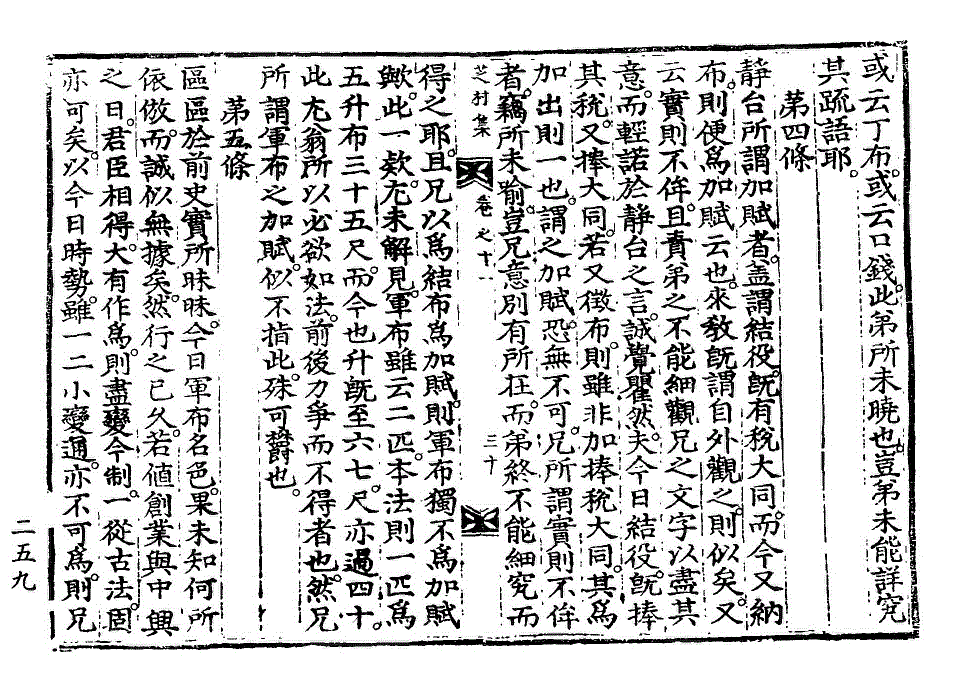 或云丁布。或云口钱。此弟所未晓也。岂弟未能详究其疏语耶。
或云丁布。或云口钱。此弟所未晓也。岂弟未能详究其疏语耶。第四条
静台所谓加赋者。盖谓结役。既有税大同。而今又纳布。则便为加赋云也。来教既谓自外观之。则似矣。又云实则不侔。且责弟之不能细观兄之文字以尽其意。而轻诺于静台之言。诚觉瞿然。夫今日结役。既捧其税。又捧大同。若又徵布。则虽非加捧税大同。其为加出则一也。谓之加赋。恐无不可。兄所谓实则不侔者。窃所未喻。岂兄意别有所在。而弟终不能细究而得之耶。且兄以为结布为加赋。则军布独不为加赋欤。此一款。尤未解见。军布虽云二匹。本法则一匹为五升布三十五尺。而今也升既至六七。尺亦过四十。此尤翁所以必欲如法。前后力争而不得者也。然兄所谓军布之加赋。似不指此。殊可郁也。
第五条
区区于前史实所昧昧。今日军布名色。果未知何所依仿。而诚似无据矣。然行之已久。若值创业与中兴之日。君臣相得。大有作为。则尽变今制。一从古法。固亦可矣。以今日时势。虽一二小变通。亦不可为。则兄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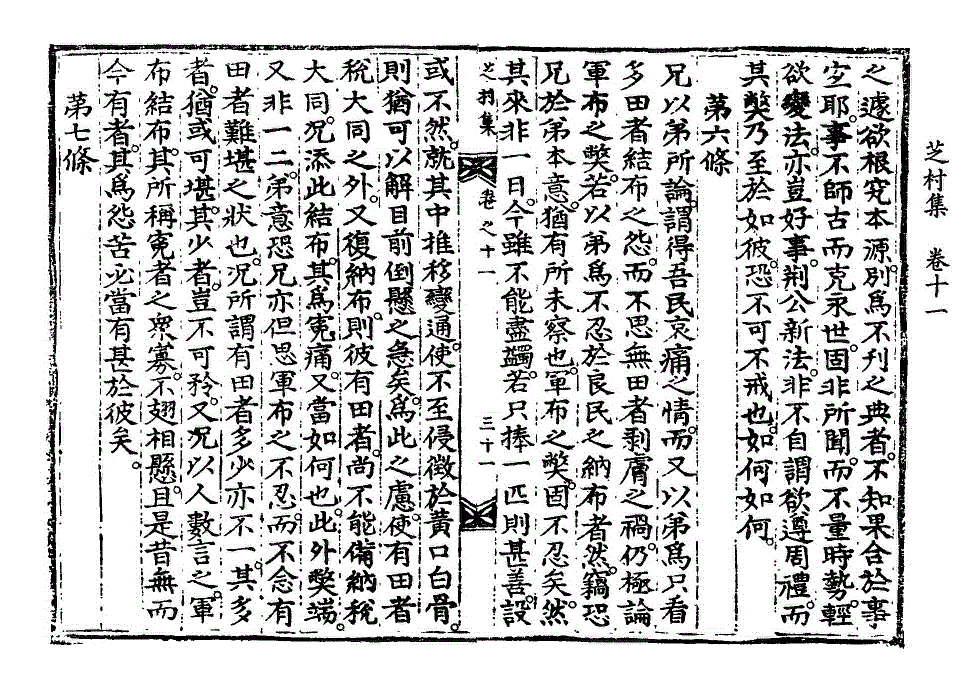 之遽欲根究本源。别为不刊之典者。不知果合于事宜耶。事不师古而克永世。固非所闻。而不量时势。轻欲变法。亦岂好事。荆公新法。非不自谓欲遵周礼。而其弊乃至于如彼。恐不可不戒也。如何如何。
之遽欲根究本源。别为不刊之典者。不知果合于事宜耶。事不师古而克永世。固非所闻。而不量时势。轻欲变法。亦岂好事。荆公新法。非不自谓欲遵周礼。而其弊乃至于如彼。恐不可不戒也。如何如何。第六条
兄以弟所论。谓得吾民哀痛之情。而又以弟为只看多田者结布之怨。而不思无田者剥肤之祸。仍极论军布之弊。若以弟为不忍于良民之纳布者然。窃恐兄于弟本意。犹有所未察也。军布之弊。固不忍矣。然其来非一日。今虽不能尽蠲。若只捧一匹则甚善。设或不然。就其中推移变通。使不至侵徵于黄口白骨。则犹可以解目前倒悬之急矣。为此之虑。使有田者税大同之外。又复纳布。则彼有田者。尚不能备纳税大同。况添此结布。其为冤痛。又当如何也。此外弊端。又非一二。弟意恐兄亦但思军布之不忍。而不念有田者难堪之状也。况所谓有田者多少亦不一。其多者。犹或可堪。其少者。岂不可矜。又况以人数言之。军布结布。其所称冤者之众寡。不翅相悬。且是昔无而今有者。其为怨苦必当有甚于彼矣。
第七条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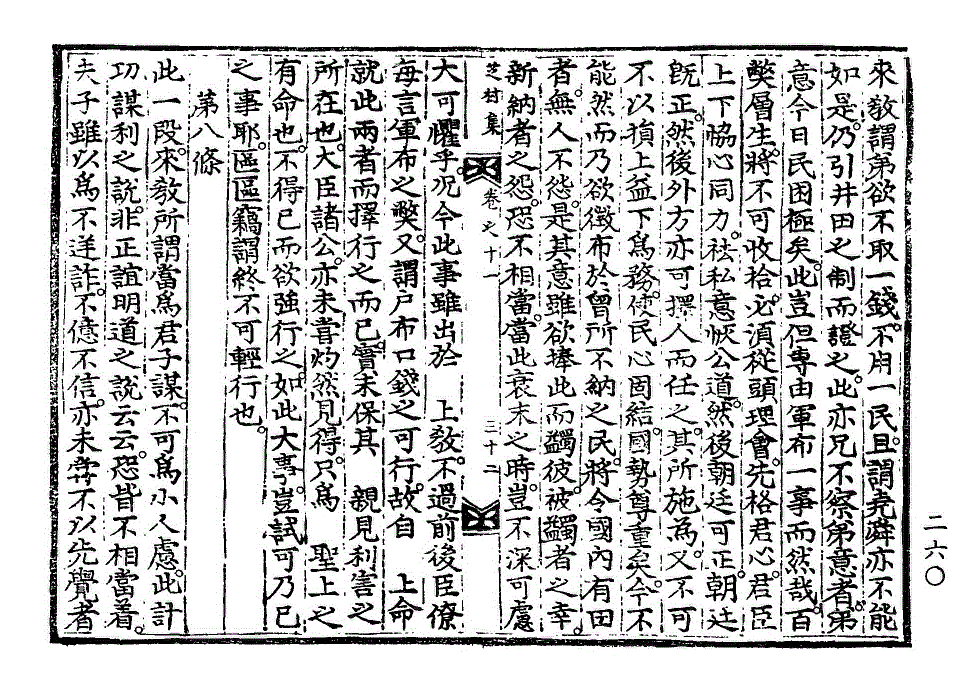 来教谓弟欲不取一钱。不用一民。且谓尧舜亦不能如是。仍引井田之制而證之。此亦兄不察弟意者。弟意今日民困极矣。此岂但专由军布一事而然哉。百弊层生。将不可收拾。必须从头理会。先格君心。君臣上下协心同力。祛私意恢公道。然后朝廷可正。朝廷既正。然后外方亦可择人而任之。其所施为。又不可不以损上益下为务。使民心固结。国势尊重矣。今不能然而乃欲徵布于曾所不纳之民。将令国内有田者。无人不怨。是其意虽欲捧此而蠲彼。被蠲者之幸。新纳者之怨。恐不相当。当此衰末之时。岂不深可虑大可惧乎。况今此事虽出于 上教。不过前后臣僚每言军布之弊。又谓户布口钱之可行。故自 上命就此两者而择行之而已。实未保其 亲见利害之所在也。大臣诸公。亦未尝灼然见得。只为 圣上之有命也。不得已而欲强行之。如此大事。岂试可乃已之事耶。区区窃谓终不可轻行也。
来教谓弟欲不取一钱。不用一民。且谓尧舜亦不能如是。仍引井田之制而證之。此亦兄不察弟意者。弟意今日民困极矣。此岂但专由军布一事而然哉。百弊层生。将不可收拾。必须从头理会。先格君心。君臣上下协心同力。祛私意恢公道。然后朝廷可正。朝廷既正。然后外方亦可择人而任之。其所施为。又不可不以损上益下为务。使民心固结。国势尊重矣。今不能然而乃欲徵布于曾所不纳之民。将令国内有田者。无人不怨。是其意虽欲捧此而蠲彼。被蠲者之幸。新纳者之怨。恐不相当。当此衰末之时。岂不深可虑大可惧乎。况今此事虽出于 上教。不过前后臣僚每言军布之弊。又谓户布口钱之可行。故自 上命就此两者而择行之而已。实未保其 亲见利害之所在也。大臣诸公。亦未尝灼然见得。只为 圣上之有命也。不得已而欲强行之。如此大事。岂试可乃已之事耶。区区窃谓终不可轻行也。第八条
此一段。来教所谓当为君子谋。不可为小人虑。此计功谋利之说。非正谊明道之说云云。恐皆不相当着。夫子虽以为不逆诈。不亿不信。亦未尝不以先觉者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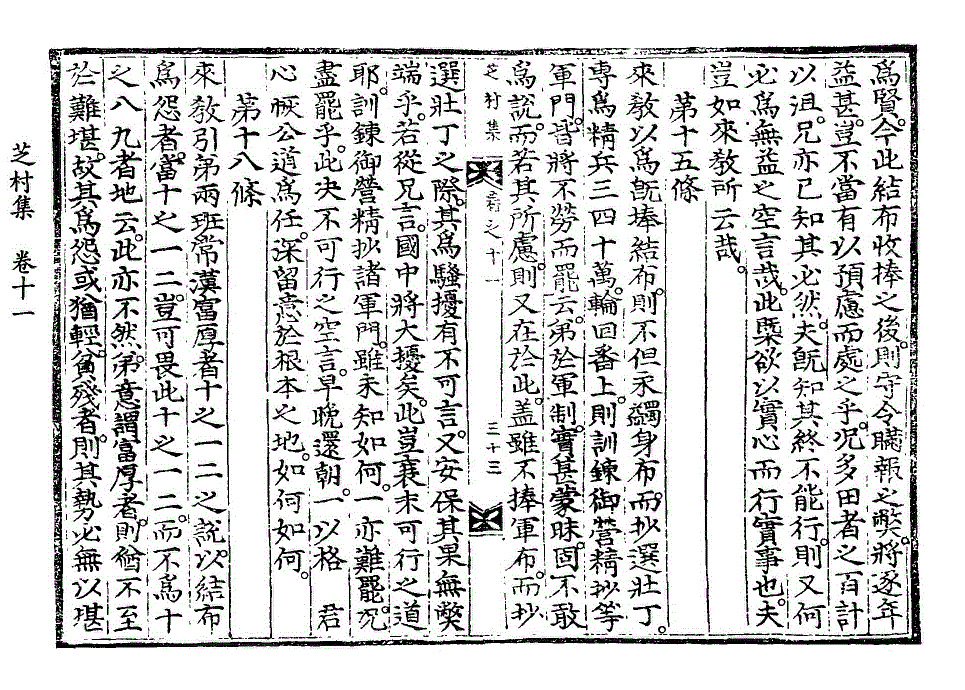 为贤。今此结布收捧之后。则守令瞒报之弊。将逐年益甚。岂不当有以预虑而处之乎。况多田者之百计以沮。兄亦已知其必然。夫既知其终不能行。则又何必为无益之空言哉。此槩欲以实心而行实事也。夫岂如来教所云哉。
为贤。今此结布收捧之后。则守令瞒报之弊。将逐年益甚。岂不当有以预虑而处之乎。况多田者之百计以沮。兄亦已知其必然。夫既知其终不能行。则又何必为无益之空言哉。此槩欲以实心而行实事也。夫岂如来教所云哉。第十五条
来教以为既捧结布。则不但永蠲身布。而抄选壮丁。专为精兵三四十万。轮回番上。则训鍊御营精抄等军门。皆将不劳而罢云。弟于军制。实甚蒙昧。固不敢为说。而若其所虑。则又在于此。盖虽不捧军布。而抄选壮丁之际。其为骚扰有不可言。又安保其果无弊端乎。若从兄言。国中将大扰矣。此岂衰末可行之道耶。训鍊御营精抄诸军门。虽未知如何。一亦难罢。况尽罢乎。此决不可行之空言。早晚还朝。一以格 君心恢公道为任。深留意于根本之地。如何如何。
第十八条
来教引弟两班常汉富厚者十之一二之说。以结布为怨者。当十之一二。岂可畏此十之一二。而不为十之八九者地云。此亦不然。弟意谓富厚者。则犹不至于难堪。故其为怨或犹轻。贫残者。则其势必无以堪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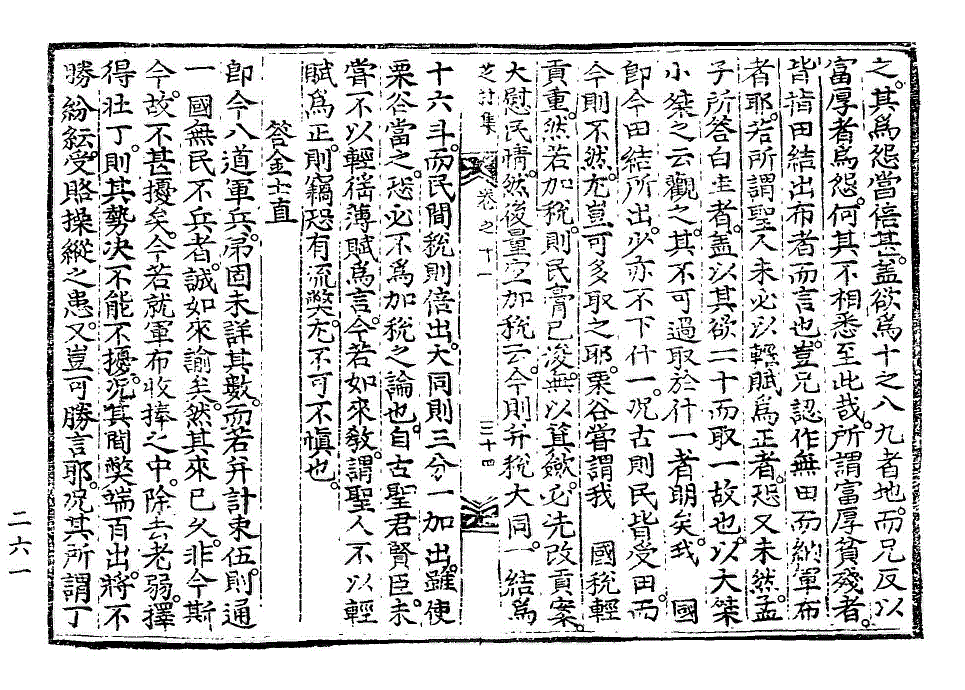 之。其为怨当倍甚。盖欲为十之八九者地。而兄反以富厚者为怨。何其不相悉至此哉。所谓富厚贫残者。皆指田结出布者而言也。岂兄认作无田而纳军布者耶。若所谓圣人未必以轻赋为正者。恐又未然。孟子所答白圭者。盖以其欲二十而取一故也。以大桀小桀之云观之。其不可过取于什一者明矣。我 国即今田结所出。少亦不下什一。况古则民皆受田。而今则不然。尤岂可多取之耶。栗谷尝谓我 国税轻贡重。然若加税。则民膏已浚。无以箕敛。必先改贡案。大慰民情。然后量宜加税云。今则并税大同。一结为十六斗。而民间税则倍出。大同则三分一加出。虽使栗谷当之。恐必不为加税之论也。自古圣君贤臣。未尝不以轻徭薄赋为言。今若如来教。谓圣人不以轻赋为正。则窃恐有流弊。尤不可不慎也。
之。其为怨当倍甚。盖欲为十之八九者地。而兄反以富厚者为怨。何其不相悉至此哉。所谓富厚贫残者。皆指田结出布者而言也。岂兄认作无田而纳军布者耶。若所谓圣人未必以轻赋为正者。恐又未然。孟子所答白圭者。盖以其欲二十而取一故也。以大桀小桀之云观之。其不可过取于什一者明矣。我 国即今田结所出。少亦不下什一。况古则民皆受田。而今则不然。尤岂可多取之耶。栗谷尝谓我 国税轻贡重。然若加税。则民膏已浚。无以箕敛。必先改贡案。大慰民情。然后量宜加税云。今则并税大同。一结为十六斗。而民间税则倍出。大同则三分一加出。虽使栗谷当之。恐必不为加税之论也。自古圣君贤臣。未尝不以轻徭薄赋为言。今若如来教。谓圣人不以轻赋为正。则窃恐有流弊。尤不可不慎也。答金士直
即今八道军兵。弟固未详其数。而若并计束伍。则通一国无民不兵者。诚如来谕矣。然其来已久。非今斯今。故不甚扰矣。今若就军布收捧之中。除去老弱。择得壮丁。则其势决不能不扰。况其间弊端百出。将不胜纷纭。受赂操纵之患。又岂可胜言耶。况其所谓丁
芝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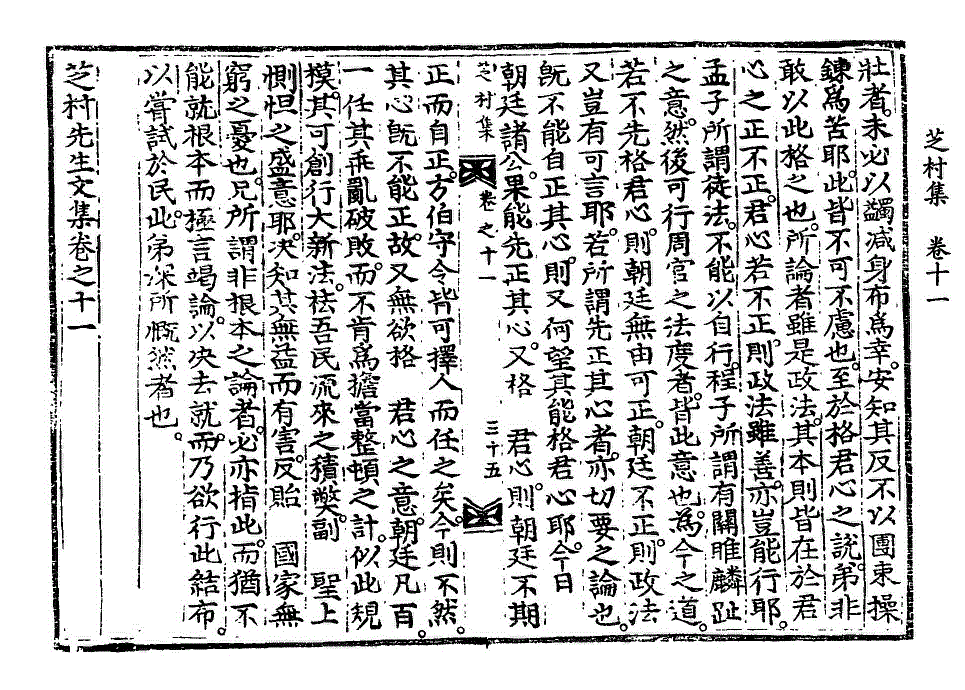 壮者。未必以蠲减身布为幸。安知其反不以团束操鍊为苦耶。此皆不可不虑也。至于格君心之说。弟非敢以此格之也。所论者虽是政法。其本则皆在于君心之正不正。君心若不正。则政法虽善。亦岂能行耶。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者。皆此意也。为今之道。若不先格君心。则朝廷无由可正。朝廷不正。则政法又岂有可言耶。若所谓先正其心者。亦切要之论也。既不能自正其心。则又何望其能格君心耶。今日 朝廷诸公。果能先正其心。又格 君心。则朝廷不期正而自正。方伯守令皆可择人而任之矣。今则不然。其心既不能正。故又无欲格 君心之意。朝廷凡百。一任其乖乱破败。而不肯为担当整顿之计。似此规模。其可创行大新法。祛吾民流来之积弊。副 圣上恻怛之盛意耶。决知其无益而有害。反贻 国家无穷之忧也。兄所谓非根本之论者。必亦指此。而犹不能就根本而极言竭论。以决去就。而乃欲行此结布。以尝试于民。此弟深所慨然者也。
壮者。未必以蠲减身布为幸。安知其反不以团束操鍊为苦耶。此皆不可不虑也。至于格君心之说。弟非敢以此格之也。所论者虽是政法。其本则皆在于君心之正不正。君心若不正。则政法虽善。亦岂能行耶。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者。皆此意也。为今之道。若不先格君心。则朝廷无由可正。朝廷不正。则政法又岂有可言耶。若所谓先正其心者。亦切要之论也。既不能自正其心。则又何望其能格君心耶。今日 朝廷诸公。果能先正其心。又格 君心。则朝廷不期正而自正。方伯守令皆可择人而任之矣。今则不然。其心既不能正。故又无欲格 君心之意。朝廷凡百。一任其乖乱破败。而不肯为担当整顿之计。似此规模。其可创行大新法。祛吾民流来之积弊。副 圣上恻怛之盛意耶。决知其无益而有害。反贻 国家无穷之忧也。兄所谓非根本之论者。必亦指此。而犹不能就根本而极言竭论。以决去就。而乃欲行此结布。以尝试于民。此弟深所慨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