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x 页
定斋别集卷之四
坎流编[上]
坎流编[上]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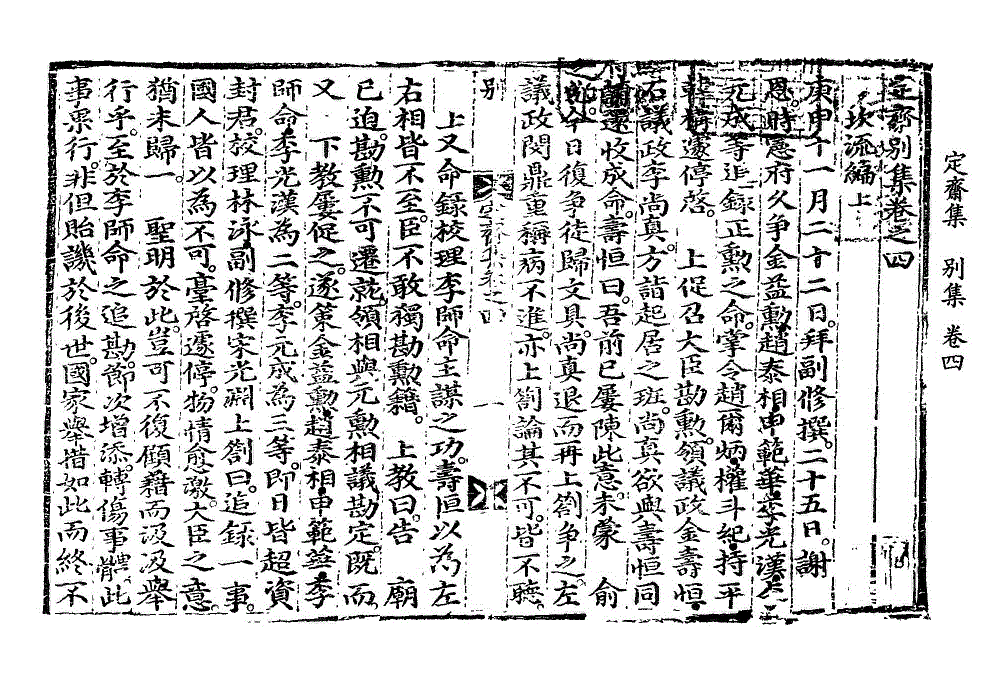 庚申十一月
庚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拜副修撰。二十五日。谢 恩。时宪府久争金益勋,赵泰相,申范华,李光汉,李元成等追录正勋之命。掌令赵尔炳,权斗纪,持平韩构遽停启。 上促召大臣勘勋。领议政金寿恒,右议政李尚真。方诣起居之班。尚真欲与寿恒同请还收成命。寿恒曰。吾前已屡陈此意。未蒙 俞允。今日复争徒归文具。尚真退而再上劄争之。左议政闵鼎重称病不进。亦上劄论其不可。皆不听。 上又命录校理李师命主谋之功。寿恒以为左右相皆不至。臣不敢独勘勋籍。 上教曰。告 庙已迫。勘勋不可迁就。领相与元勋相议勘定。既而。又 下教屡促之。遂策金益勋,赵泰相,申范华,李师命,李光汉为二等。李元成为三等。即日皆超资封君。校理林泳,副修撰宋光渊上劄曰。追录一事。国人皆以为不可。台启遽停。物情愈激。大臣之意。犹未归一。 圣明于此。岂可不复顾藉而汲汲举行乎。至于李师命之追勘。节次增添。转伤事体。此事果行。非但贻讥于后世。国家举措如此而终不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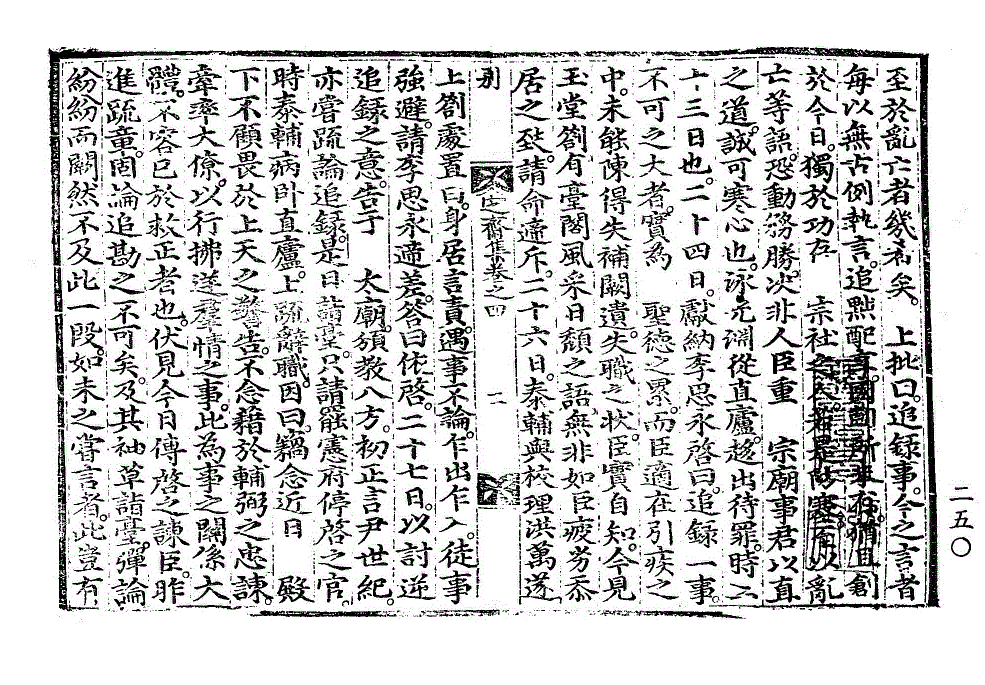 至于乱亡者几希矣。 上批曰。追录事。今之言者每以无古例执言。追黜配享。国朝所未有。犹且创于今日。独于功存 宗社之人。若是防塞。至以乱亡等语。恐动务胜。决非人臣重 宗庙事君以直之道。诚可寒心也。泳,光渊从直庐。趍出待罪。时二十三日也。二十四日。献纳李思永启曰。追录一事。不可之大者。实为 圣德之累。而臣适在引疾之中。未能陈得失补阙遗。失职之状。臣实自知。今见玉堂劄。有台阁风采日颓之语。无非如臣疲劣忝居之致。请命遆斥。二十六日。泰辅与校理洪万遂上劄处置曰。身居言责。遇事不论。乍出乍入。徒事强避。请李思永遆差。答曰依启。二十七日。以讨逆追录之意。告于 太庙。颁教八方。初正言尹世纪。亦尝疏论追录。是日诣台。只请罢宪府停启之官。时泰辅病卧直庐。上疏辞职。因曰。窃念近日 殿下不顾畏于上天之警告。不念藉于辅弼之忠谏。牵率大僚。以行拂逆群情之事。此为事之关系大体。不容已于救正者也。伏见今日传启之谏臣。昨进疏章。固论追勘之不可矣。及其袖草诣台。弹论纷纷而阙然不及此一段。如未之尝言者。此岂有
至于乱亡者几希矣。 上批曰。追录事。今之言者每以无古例执言。追黜配享。国朝所未有。犹且创于今日。独于功存 宗社之人。若是防塞。至以乱亡等语。恐动务胜。决非人臣重 宗庙事君以直之道。诚可寒心也。泳,光渊从直庐。趍出待罪。时二十三日也。二十四日。献纳李思永启曰。追录一事。不可之大者。实为 圣德之累。而臣适在引疾之中。未能陈得失补阙遗。失职之状。臣实自知。今见玉堂劄。有台阁风采日颓之语。无非如臣疲劣忝居之致。请命遆斥。二十六日。泰辅与校理洪万遂上劄处置曰。身居言责。遇事不论。乍出乍入。徒事强避。请李思永遆差。答曰依启。二十七日。以讨逆追录之意。告于 太庙。颁教八方。初正言尹世纪。亦尝疏论追录。是日诣台。只请罢宪府停启之官。时泰辅病卧直庐。上疏辞职。因曰。窃念近日 殿下不顾畏于上天之警告。不念藉于辅弼之忠谏。牵率大僚。以行拂逆群情之事。此为事之关系大体。不容已于救正者也。伏见今日传启之谏臣。昨进疏章。固论追勘之不可矣。及其袖草诣台。弹论纷纷而阙然不及此一段。如未之尝言者。此岂有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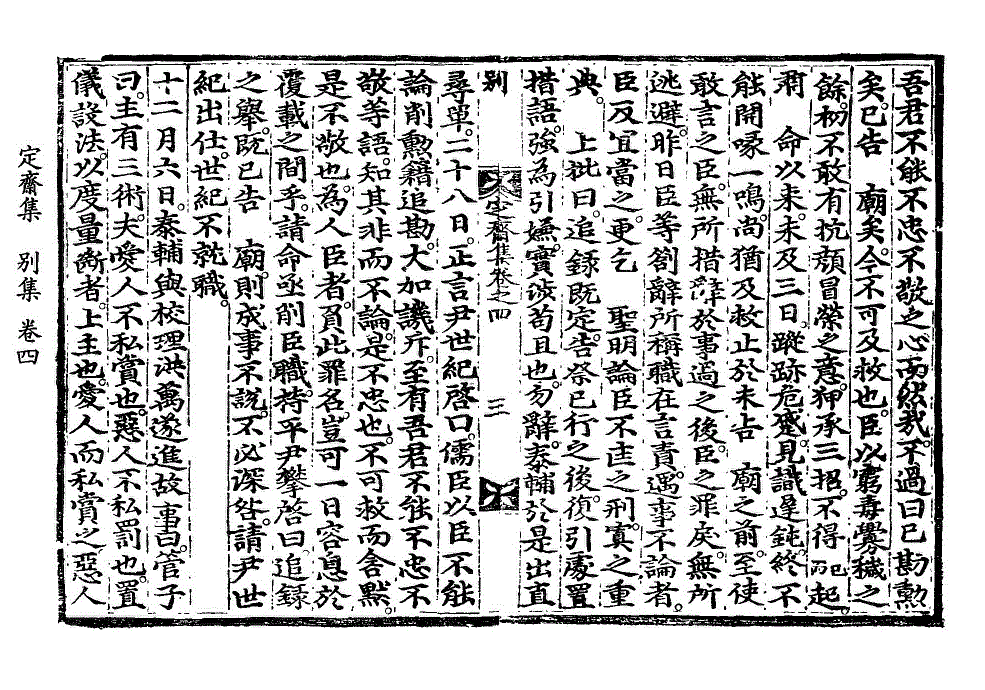 吾君不能不忠不敬之心而然哉。不过曰已勘勋矣。已告 庙矣。今不可及救也。臣以穷毒衅秽之馀。初不敢有抗颜冒荣之意。狎承三招。不得已而起。肃 命以来。未及三日。踪迹危蹙。见识迟钝。终不能开喙一鸣。尚犹及救止于未告 庙之前。至使敢言之臣。无所措辞于事过之后。臣之罪戾。无所逃避。昨日臣等劄辞所称职在言责。遇事不论者。臣反宜当之。更乞 圣明论臣不匡之刑。寘之重典。 上批曰。追录既定。告祭已行之后。复引处置措语。强为引嫌。实涉苟且也。勿辞。泰辅于是出直寻单。二十八日。正言尹世纪启曰。儒臣以臣不能论削勋籍追勘。大加讥斥。至有吾君不能不忠不敬等语。知其非而不论。是不忠也。不可救而含默。是不敬也。为人臣者。负此罪名。岂可一日容息于覆载之间乎。请命亟削臣职。持平尹攀启曰。追录之举。既已告 庙。则成事不说。不必深咎。请尹世纪出仕。世纪不就职。
吾君不能不忠不敬之心而然哉。不过曰已勘勋矣。已告 庙矣。今不可及救也。臣以穷毒衅秽之馀。初不敢有抗颜冒荣之意。狎承三招。不得已而起。肃 命以来。未及三日。踪迹危蹙。见识迟钝。终不能开喙一鸣。尚犹及救止于未告 庙之前。至使敢言之臣。无所措辞于事过之后。臣之罪戾。无所逃避。昨日臣等劄辞所称职在言责。遇事不论者。臣反宜当之。更乞 圣明论臣不匡之刑。寘之重典。 上批曰。追录既定。告祭已行之后。复引处置措语。强为引嫌。实涉苟且也。勿辞。泰辅于是出直寻单。二十八日。正言尹世纪启曰。儒臣以臣不能论削勋籍追勘。大加讥斥。至有吾君不能不忠不敬等语。知其非而不论。是不忠也。不可救而含默。是不敬也。为人臣者。负此罪名。岂可一日容息于覆载之间乎。请命亟削臣职。持平尹攀启曰。追录之举。既已告 庙。则成事不说。不必深咎。请尹世纪出仕。世纪不就职。庚申十二月
六日。泰辅与校理洪万遂进故事曰。管子曰。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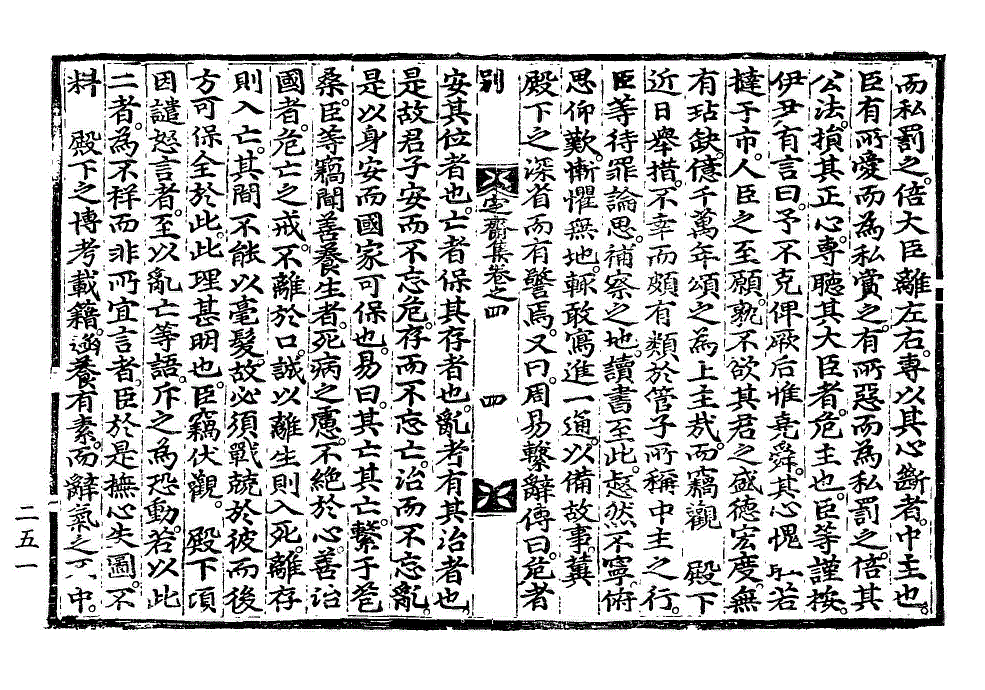 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臣等谨按。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韨。人臣之至愿。孰不欲其君之盛德宏度。无有玷缺。亿千万年颂之为上主哉。而窃观 殿下近日举措。不幸而颇有类于管子所称中主之行。臣等待罪论思。补察之地。读书至此。惄然不宁。俯思仰叹。惭惧无地。辄敢写进一通。以备故事。冀 殿下之深省而有警焉。又曰。周易系辞传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臣等窃闻善养生者。死病之虑。不绝于心。善治国者。危亡之戒。不离于口。诚以离生则入死。离存则入亡。其间不能以毫发。故必须战兢于彼而后方可保全于此。此理甚明也。臣窃伏观。 殿下顷因谴怒言者。至以乱亡等语。斥之为恐动。若以此二者。为不祥而非所宜言者。臣于是抚心失图。不料 殿下之博考载籍。涵养有素。而辞气之不中。
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臣等谨按。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韨。人臣之至愿。孰不欲其君之盛德宏度。无有玷缺。亿千万年颂之为上主哉。而窃观 殿下近日举措。不幸而颇有类于管子所称中主之行。臣等待罪论思。补察之地。读书至此。惄然不宁。俯思仰叹。惭惧无地。辄敢写进一通。以备故事。冀 殿下之深省而有警焉。又曰。周易系辞传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臣等窃闻善养生者。死病之虑。不绝于心。善治国者。危亡之戒。不离于口。诚以离生则入死。离存则入亡。其间不能以毫发。故必须战兢于彼而后方可保全于此。此理甚明也。臣窃伏观。 殿下顷因谴怒言者。至以乱亡等语。斥之为恐动。若以此二者。为不祥而非所宜言者。臣于是抚心失图。不料 殿下之博考载籍。涵养有素。而辞气之不中。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2H 页
 乃至于此也。方今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国事溃裂。无可收拾。君臣上下。正当各怀其亡之戒。期致苞桑之安。若复以乱亡为讳。钳直臣之口。杜忠谏之路。则臣恐所谓乱亡之徵。或者正在于此也。夫人心有所偏系。则矫拂之来。言不择发。斯固恒情之大患。仰惟 圣度渊懿。不应有此。虽暂蹉跌于酬酢之际。必已悔悟于燕闲之中。臣等不必更有烦论于已久之后。而区区忧爱之忱。尚虑 圣明或有一毫厌闻乱亡之意。留着胸中。则实关治乱存亡安危之大机。故敢因易大传之说。缕缕至此。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
乃至于此也。方今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国事溃裂。无可收拾。君臣上下。正当各怀其亡之戒。期致苞桑之安。若复以乱亡为讳。钳直臣之口。杜忠谏之路。则臣恐所谓乱亡之徵。或者正在于此也。夫人心有所偏系。则矫拂之来。言不择发。斯固恒情之大患。仰惟 圣度渊懿。不应有此。虽暂蹉跌于酬酢之际。必已悔悟于燕闲之中。臣等不必更有烦论于已久之后。而区区忧爱之忱。尚虑 圣明或有一毫厌闻乱亡之意。留着胸中。则实关治乱存亡安危之大机。故敢因易大传之说。缕缕至此。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十七日。左相以泰辅所撰进议政府率百官 永昭殿进香祭文。不合于臣僚进香之文体。请改命他人撰进。于是上疏辞职。不许。复寻单。二十七日。遆付典籍。
二十一日。上疏陈情。乞畀县印。以养老母。二十五日 教曰。值此乏人之时。经幄之臣。不可许出。依朴泰逊例。令该曹题给衣资食物。户曹输送米十石,绵䌷十五匹,豕一口,石鱼二十束,民鱼十尾。辛酉正月二日。同宗兄泰逊。奉笺谢 恩。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2L 页
 辛酉正月
辛酉正月十九日。拜副修撰。承 牌谢 恩。
初 上元年乙卯。吴始寿傧清人之来吊者。还奏言到龙川。通官张孝礼语诸译曰。皇帝以 先国王有积年沉痼之疾。而事大之诚不替。又受制强臣。事有不得自由。故特用异典。赐祭二度。黄海监司尹阶。亦见孝礼。闻此言矣。尹阶再上疏。自辨不闻。台谏论阶诬罔。拿问而流之。时窃议者皆以为始寿自造此言。谋以挤陷向日当国者。庚申。始寿等败。言者请究覈其事。庙堂请先令使北者。问诸张孝礼。孝礼答云。吾但戏言。朝鲜两班鼻强。未尝有受制强臣之语。乃鞫问始寿及译官朴廷荩,安日新,卞尔辅,金起门,金裕显等。诸译皆言当时但闻皇帝以 先王至诚事大。而 生沉病。享年不永。故别为致祭。及孝礼有尔国两班不善之语。此外未闻他语。始寿抵言朴廷荩安日新辈。同来传臣强之语及他援引甚多。卒未有为始寿作證者。鞫厅大臣金寿恒等。以为始寿情状。败露无馀。而不肯就服。宜严讯以得其情。而始寿尝为大臣。不可加刑。合有酌处之道。 上命始寿赐死。诸译定配。两司并请严鞫始寿。以正邦刑。及诸译必为符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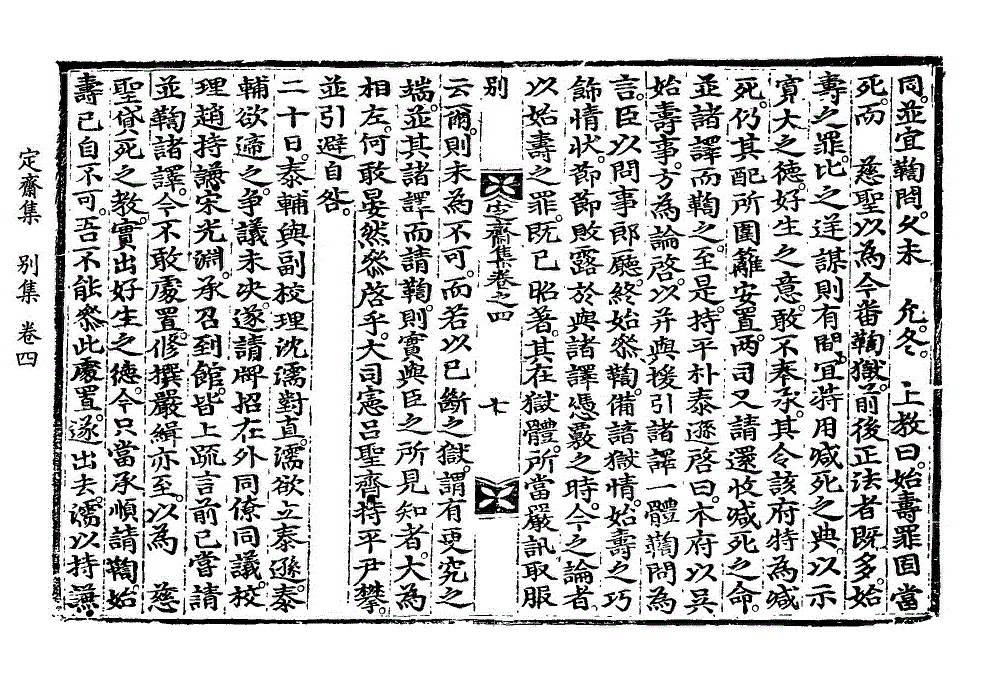 同。并宜鞫问。久未 允。冬。 上教曰。始寿罪固当死。而 慈圣以为今番鞫狱。前后正法者既多。始寿之罪。比之逆谋则有间。宜特用减死之典。以示宽大之德。好生之意。敢不奉承。其令该府特为减死。仍其配所围篱安置。两司又请还收减死之命。并诸译而鞫之。至是。持平朴泰逊启曰。本府以吴始寿事。方为论启。以并与援引诸译一体鞫问为言。臣以问事郎厅。终始参鞫。备谙狱情。始寿之巧饰情状。节节败露于与诸译凭覈之时。今之论者。以始寿之罪。既已昭著。其在狱体。所当严讯取服云尔。则未为不可。而若以已断之狱。谓有更究之端。并其诸译而请鞫。则实与臣之所见知者。大为相左。何敢晏然参启乎。大司宪吕圣齐,持平尹攀。并引避自咎。
同。并宜鞫问。久未 允。冬。 上教曰。始寿罪固当死。而 慈圣以为今番鞫狱。前后正法者既多。始寿之罪。比之逆谋则有间。宜特用减死之典。以示宽大之德。好生之意。敢不奉承。其令该府特为减死。仍其配所围篱安置。两司又请还收减死之命。并诸译而鞫之。至是。持平朴泰逊启曰。本府以吴始寿事。方为论启。以并与援引诸译一体鞫问为言。臣以问事郎厅。终始参鞫。备谙狱情。始寿之巧饰情状。节节败露于与诸译凭覈之时。今之论者。以始寿之罪。既已昭著。其在狱体。所当严讯取服云尔。则未为不可。而若以已断之狱。谓有更究之端。并其诸译而请鞫。则实与臣之所见知者。大为相左。何敢晏然参启乎。大司宪吕圣齐,持平尹攀。并引避自咎。二十日。泰辅与副校理沈濡对直。濡欲立泰逊。泰辅欲遆之。争议未决。遂请牌招在外同僚同议。校理赵持谦,宋光渊。承召到馆。皆上疏言前已尝请并鞫诸译。今不敢处置。修撰严缉亦至。以为 慈圣贷死之教。实出好生之德。今只当承顺请鞫。始寿已自不可。吾不能参此处置。遂出去。濡以持谦,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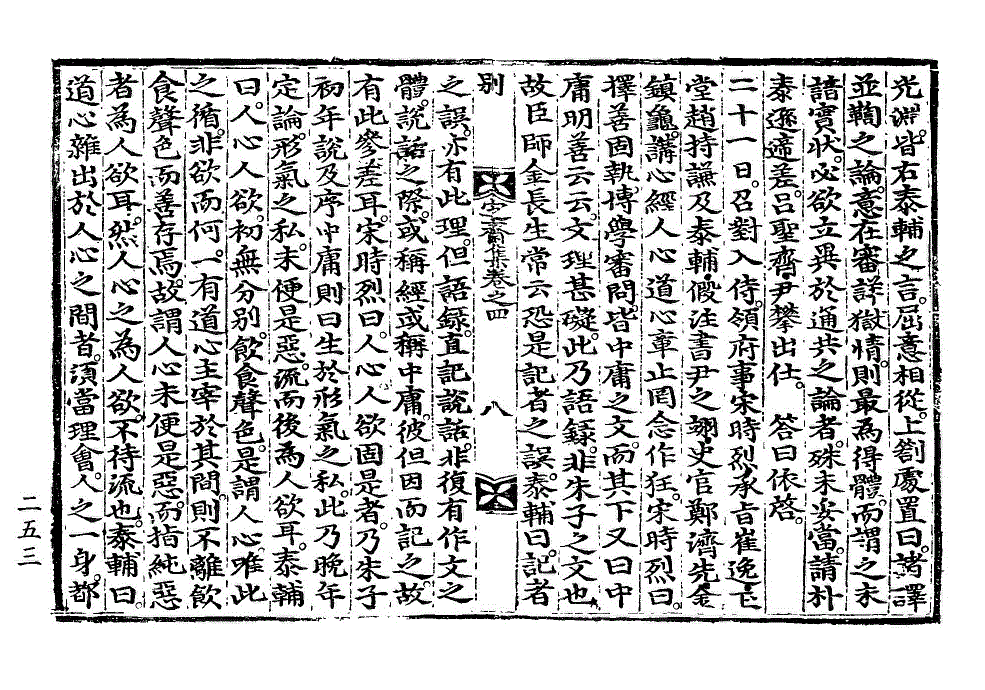 光渊。皆右泰辅之言。屈意相从。上劄处置曰。诸译并鞫之论。意在审详狱情。则最为得体。而谓之未谙实状。必欲立异于通共之论者。殊未妥当。请朴泰逊遆差。吕圣齐,尹攀出仕。 答曰依启。
光渊。皆右泰辅之言。屈意相从。上劄处置曰。诸译并鞫之论。意在审详狱情。则最为得体。而谓之未谙实状。必欲立异于通共之论者。殊未妥当。请朴泰逊遆差。吕圣齐,尹攀出仕。 答曰依启。二十一日。召对入侍。领府事宋时烈,承旨崔逸,玉堂赵持谦及泰辅,假注书尹之翊,史官郑济先,金镇龟。讲心经人心道心章止罔念作狂。宋时烈曰。择善固执。博学审问。皆中庸之文。而其下又曰中庸明善云云。文理甚碍。此乃语录。非朱子之文也。故臣师金长生常云恐是记者之误。泰辅曰。记者之误。亦有此理。但语录。直记说话。非复有作文之体。说话之际。或称经或称中庸。彼但因而记之。故有此参差耳。宋时烈曰。人心。人欲固是者。乃朱子初年说及序中庸则曰生于形气之私。此乃晚年定论。形气之私。未便是恶。流而后为人欲耳。泰辅曰。人心人欲。初无分别。饮食声色。是谓人心。唯此之循。非欲而何。一有道心主宰于其间。则不离饮食声色而善存焉。故谓人心未便是恶。而指纯恶者为人欲耳。然人心之为人欲。不待流也。泰辅曰。道心杂出于人心之间者。须当理会。人之一身。都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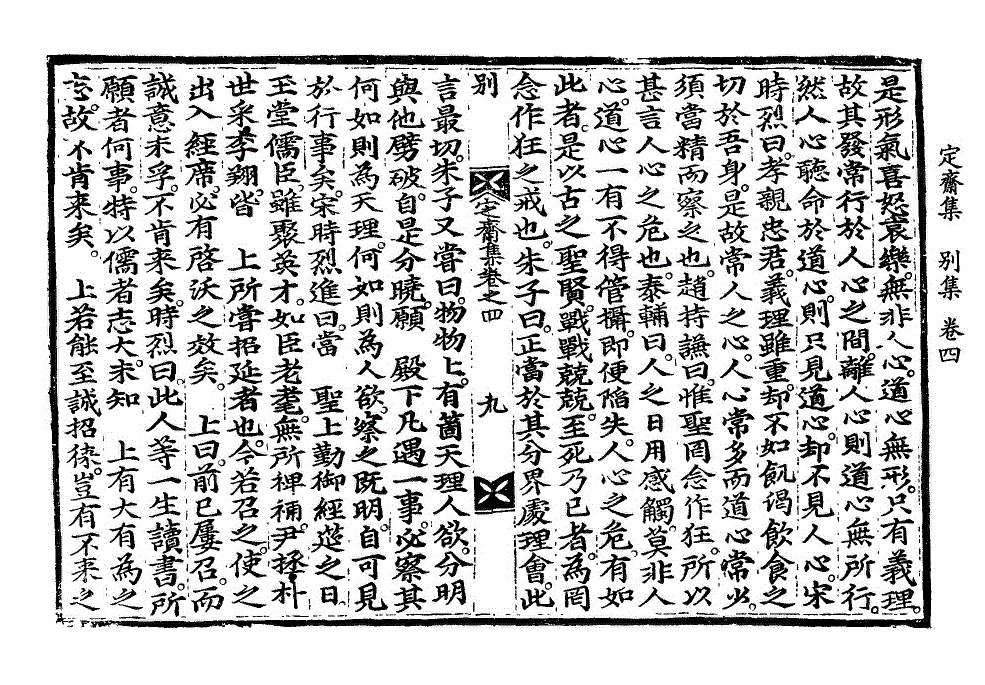 是形气喜怒哀乐。无非人心。道心无形。只有义理。故其发常行于人心之间。离人心则道心无所行。然人心听命于道心。则只见道心。却不见人心。宋时烈曰。孝亲忠君。义理虽重。却不如饥渴饮食之切于吾身。是故常人之心。人心常多而道心常少。须当精而察之也。赵持谦曰。惟圣罔念作狂。所以甚言人心之危也。泰辅曰。人之日用感触。莫非人心。道心一有不得管摄。即便陷失。人心之危。有如此者。是以古之圣贤。战战兢兢。至死乃已者。为罔念作狂之戒也。朱子曰。正当于其分界处理会。此言最切。朱子又尝曰。物物上。有个天理人欲。分明与他劈破。自是分晓。愿 殿下凡遇一事。必察其何如则为天理。何如则为人欲。察之既明。自可见于行事矣。宋时烈进曰。当 圣上勤御经筵之日。玉堂儒臣。虽聚英才。如臣老耄。无所裨补。尹拯,朴世采,李翔。皆 上所尝招延者也。今若召之。使之出入经席。必有启沃之效矣。 上曰。前已屡召。而诚意未孚。不肯来矣。时烈曰。此人等一生读书。所愿者何事。特以儒者志大。未知 上有大有为之志。故不肯来矣。 上若能至诚招徕。岂有不来之
是形气喜怒哀乐。无非人心。道心无形。只有义理。故其发常行于人心之间。离人心则道心无所行。然人心听命于道心。则只见道心。却不见人心。宋时烈曰。孝亲忠君。义理虽重。却不如饥渴饮食之切于吾身。是故常人之心。人心常多而道心常少。须当精而察之也。赵持谦曰。惟圣罔念作狂。所以甚言人心之危也。泰辅曰。人之日用感触。莫非人心。道心一有不得管摄。即便陷失。人心之危。有如此者。是以古之圣贤。战战兢兢。至死乃已者。为罔念作狂之戒也。朱子曰。正当于其分界处理会。此言最切。朱子又尝曰。物物上。有个天理人欲。分明与他劈破。自是分晓。愿 殿下凡遇一事。必察其何如则为天理。何如则为人欲。察之既明。自可见于行事矣。宋时烈进曰。当 圣上勤御经筵之日。玉堂儒臣。虽聚英才。如臣老耄。无所裨补。尹拯,朴世采,李翔。皆 上所尝招延者也。今若召之。使之出入经席。必有启沃之效矣。 上曰。前已屡召。而诚意未孚。不肯来矣。时烈曰。此人等一生读书。所愿者何事。特以儒者志大。未知 上有大有为之志。故不肯来矣。 上若能至诚招徕。岂有不来之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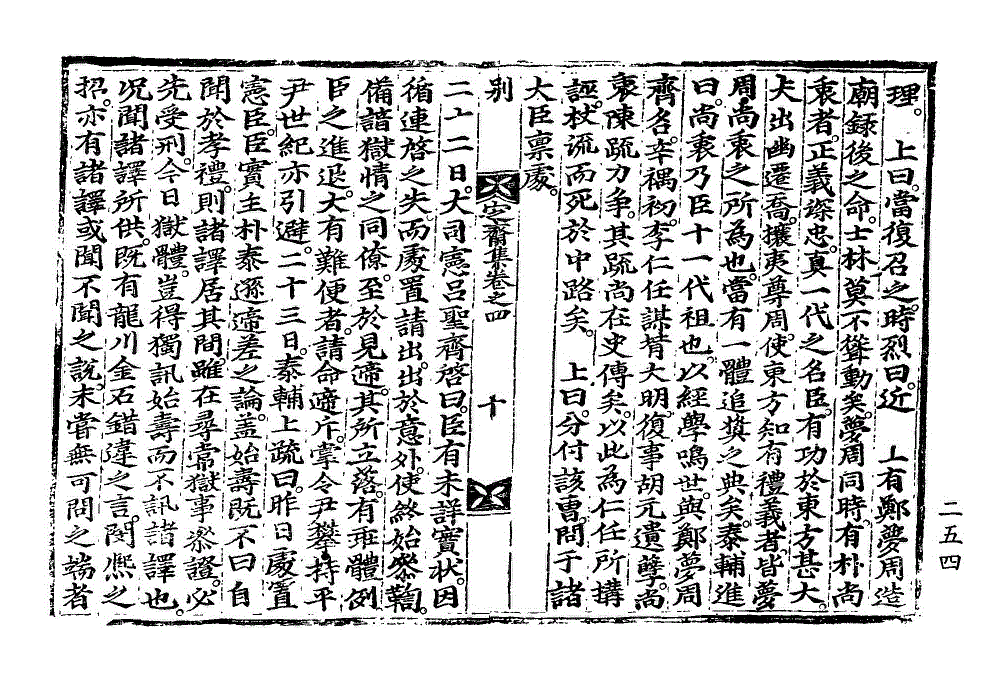 理。 上曰。当复召之。时烈曰。近 上有郑梦周造庙录后之命。士林莫不耸动矣。梦周同时。有朴尚衷者。正义深忠。真一代之名臣。有功于东方甚大。夫出幽迁乔。攘夷尊周。使东方知有礼义者。皆梦周,尚衷之所为也。当有一体追奖之典矣。泰辅进曰。尚衷乃臣十一代祖也。以经学鸣世。与郑梦周齐名。辛祦初。李仁任谋背大明。复事胡元遗孽。尚衷陈疏力争。其疏尚在史传矣。以此为仁任所搆诬。杖流而死于中路矣。 上曰。分付该曹。问于诸大臣禀处。
理。 上曰。当复召之。时烈曰。近 上有郑梦周造庙录后之命。士林莫不耸动矣。梦周同时。有朴尚衷者。正义深忠。真一代之名臣。有功于东方甚大。夫出幽迁乔。攘夷尊周。使东方知有礼义者。皆梦周,尚衷之所为也。当有一体追奖之典矣。泰辅进曰。尚衷乃臣十一代祖也。以经学鸣世。与郑梦周齐名。辛祦初。李仁任谋背大明。复事胡元遗孽。尚衷陈疏力争。其疏尚在史传矣。以此为仁任所搆诬。杖流而死于中路矣。 上曰。分付该曹。问于诸大臣禀处。二十二日。大司宪吕圣齐启曰。臣有未详实状。因循连启之失。而处置请出。出于意外。使终始参鞫。备谙狱情之同僚。至于见遆。其所立落。有乖体例。臣之进退。大有难便者。请命遆斥。掌令尹攀,持平尹世纪亦引避。二十三日。泰辅上疏曰。昨日处置宪臣。臣实主朴泰逊遆差之论。盖始寿既不曰自闻于孝礼。则诸译居其间。虽在寻常狱事参證。必先受刑。今日狱体。岂得独讯始寿而不讯诸译也。况闻诸译所供。既有龙川金石错违之言。闵熙之招。亦有诸译或闻不闻之说。未尝无可问之端者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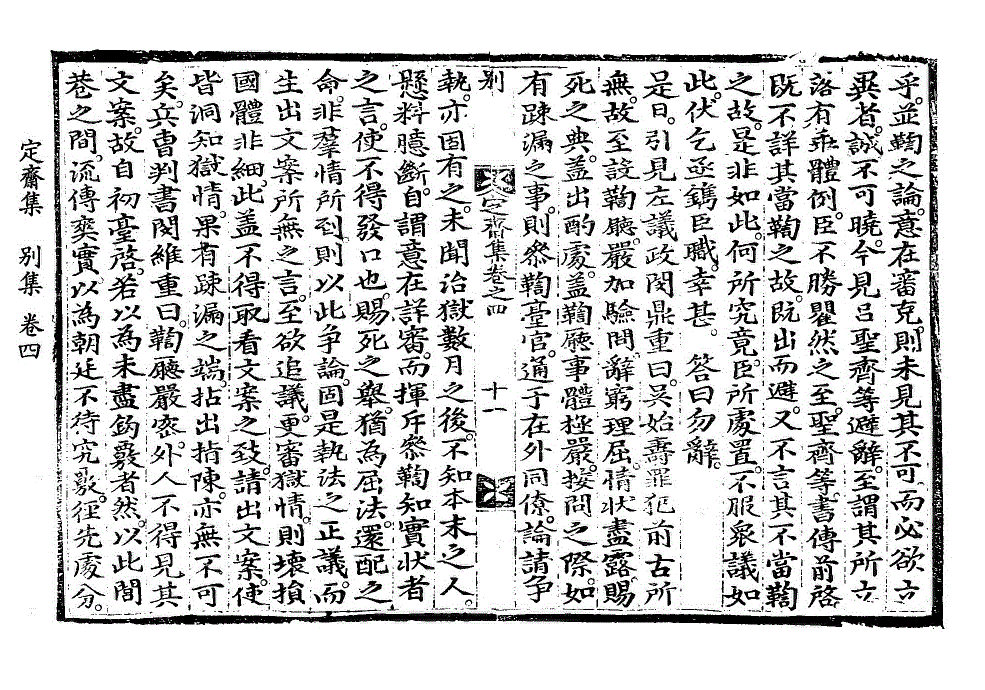 乎。并鞫之论。意在审克。则未见其不可。而必欲立异者。诚不可晓。今见吕圣齐等避辞。至谓其所立落有乖体例。臣不胜瞿然之至。圣齐等。书传前启。既不详其当鞫之故。既出而避。又不言其不当鞫之故。是非如此。何所究竟。臣所处置。不服众议如此。伏乞亟镌臣职。幸甚。 答曰勿辞。
乎。并鞫之论。意在审克。则未见其不可。而必欲立异者。诚不可晓。今见吕圣齐等避辞。至谓其所立落有乖体例。臣不胜瞿然之至。圣齐等。书传前启。既不详其当鞫之故。既出而避。又不言其不当鞫之故。是非如此。何所究竟。臣所处置。不服众议如此。伏乞亟镌臣职。幸甚。 答曰勿辞。是日。引见左议政闵鼎重曰。吴始寿罪犯前古所无。故至设鞫厅。严加验问。辞穷理屈。情状尽露。赐死之典。盖出酌处。盖鞫厅事体极严。按问之际。如有疏漏之事。则参鞫台官。通于在外同僚。论请争执。亦固有之。未闻治狱数月之后。不知本末之人。悬料臆断。自谓意在详审。而挥斥参鞫知实状者之言。使不得发口也。赐死之举。犹为屈法。还配之命。非群情所到。则以此争论。固是执法之正议。而生出文案所无之言。至欲追议。更审狱情。则坏损国体非细。此盖不得取看文案之致。请出文案。使皆洞知狱情。果有疏漏之端。拈出指陈。亦无不可矣。兵曹判书闵维重曰。鞫厅严密。外人不得见其文案。故自初台启。若以为未尽钩覈者然。以此闾巷之间。流传爽实。以为朝廷不待究覈。径先处分。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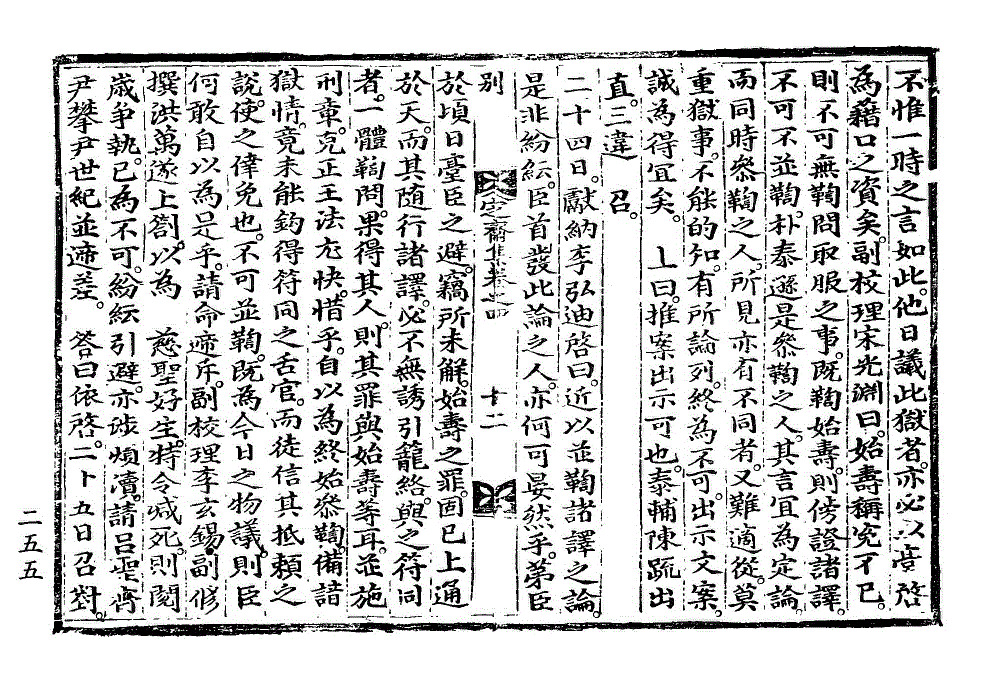 不惟一时之言如此。他日议此狱者。亦必以台启为藉口之资矣。副校理宋光渊曰。始寿称冤不已。则不可无鞫问取服之事。既鞫始寿。则傍證诸译。不可不并鞫。朴泰逊是参鞫之人。其言宜为定论。而同时参鞫之人。所见亦有不同者。又难适从。莫重狱事。不能的知。有所论列。终为不可。出示文案。诚为得宜矣。 上曰。推案出示可也。泰辅陈疏出直。三违 召。
不惟一时之言如此。他日议此狱者。亦必以台启为藉口之资矣。副校理宋光渊曰。始寿称冤不已。则不可无鞫问取服之事。既鞫始寿。则傍證诸译。不可不并鞫。朴泰逊是参鞫之人。其言宜为定论。而同时参鞫之人。所见亦有不同者。又难适从。莫重狱事。不能的知。有所论列。终为不可。出示文案。诚为得宜矣。 上曰。推案出示可也。泰辅陈疏出直。三违 召。二十四日。献纳李弘迪启曰。近以并鞫诸译之论。是非纷纭。臣首发此论之人。亦何可晏然乎。第臣于顷日台臣之避。窃所未解。始寿之罪。固已上通于天。而其随行诸译。必不无诱引笼络。与之符同者。一体鞫问。果得其人。则其罪与始寿等耳。并施刑章。克正王法尤快。惜乎。自以为终始参鞫。备谙狱情。竟未能钩得符同之舌官。而徒信其抵赖之说。使之倖免也。不可并鞫。既为今日之物议。则臣何敢自以为是乎。请命遆斥。副校理李玄锡,副修撰洪万遂上劄。以为 慈圣好生。特令减死。则阅岁争执。已为不可。纷纭引避。亦涉烦渎。请吕圣齐尹攀尹世纪并遆差。 答曰依启。二十五日召对。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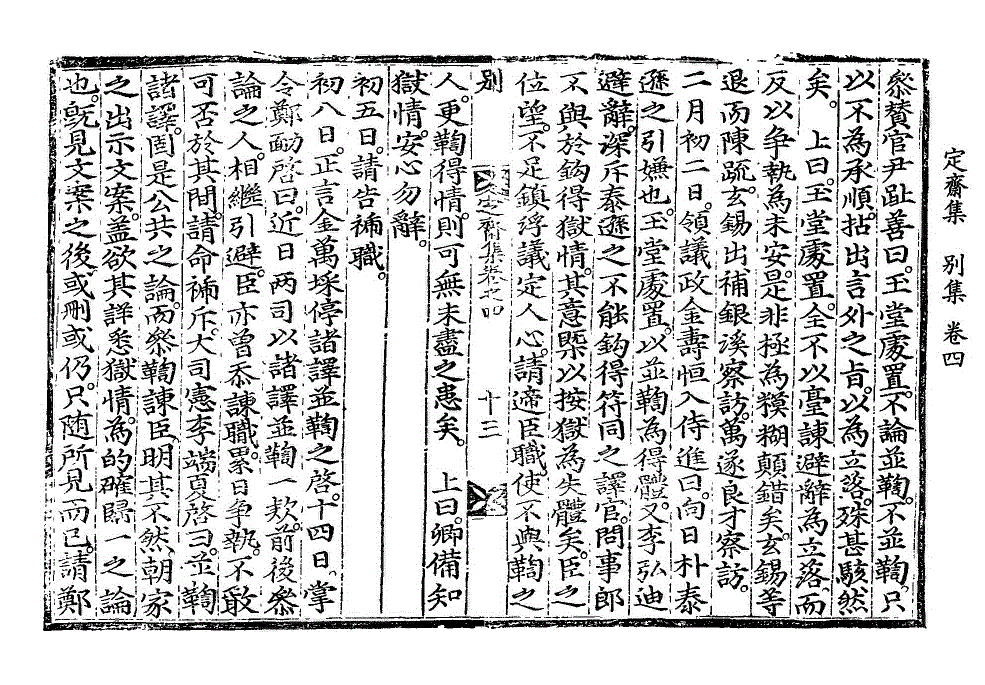 参赞官尹趾善曰。玉堂处置。不论并鞫。不并鞫。只以不为承顺。拈出言外之旨。以为立落。殊甚骇然矣。 上曰。玉堂处置。全不以台谏避辞为立落。而反以争执为未安。是非极为模糊颠错矣。玄锡等退而陈疏。玄锡出补银溪察访。万遂良才察访。
参赞官尹趾善曰。玉堂处置。不论并鞫。不并鞫。只以不为承顺。拈出言外之旨。以为立落。殊甚骇然矣。 上曰。玉堂处置。全不以台谏避辞为立落。而反以争执为未安。是非极为模糊颠错矣。玄锡等退而陈疏。玄锡出补银溪察访。万遂良才察访。辛酉二月
初二日。领议政金寿恒入侍进曰。向日朴泰逊之引嫌也。玉堂处置。以并鞫为得体。又李弘迪避辞。深斥泰逊之不能钩得符同之译官。问事郎不与于钩得狱情。其意槩以按狱为失体矣。臣之位望。不足镇浮议定人心。请遆臣职。使不与鞫之人。更鞫得情。则可无未尽之患矣。 上曰。卿备知狱情。安心勿辞。
初五日。请告褫职。
初八日。正言金万埰停诸译并鞫之启。十四日。掌令郑勔启曰。近日两司以诸译并鞫一款。前后参论之人。相继引避。臣亦曾忝谏职。累日争执。不敢可否于其间。请命褫斥。大司宪李端夏启曰。并鞫诸译。固是公共之论。而参鞫谏臣。明其不然。朝家之出示文案。盖欲其详悉狱情。为的确归一之论也。既见文案之后。或删或仍。只随所见而已。请郑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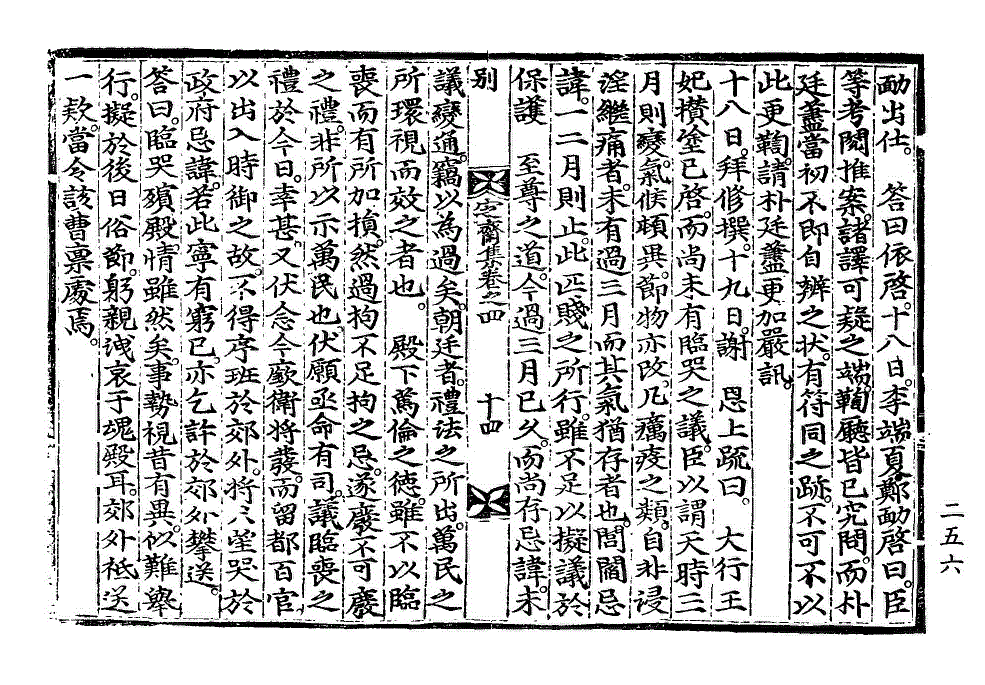 勔出仕。 答曰依启。十八日。李端夏,郑勔启曰。臣等考阅推案。诸译可疑之端。鞫厅皆已究问。而朴廷荩当初不即自辨之状。有符同之迹。不可不以此更鞫。请朴廷荩更加严讯。
勔出仕。 答曰依启。十八日。李端夏,郑勔启曰。臣等考阅推案。诸译可疑之端。鞫厅皆已究问。而朴廷荩当初不即自辨之状。有符同之迹。不可不以此更鞫。请朴廷荩更加严讯。十八日。拜修撰。十九日。谢 恩上疏曰。 大行王妃攒涂已启。而尚未有临哭之议。臣以谓天时三月则变。气候顿异。节物亦改。凡疠疫之类。自非浸淫继痛者。未有过三月而其气犹存者也。闾阎忌讳。一二月则止。此匹贱之所行。虽不足以拟议于保护 至尊之道。今过三月已久。而尚存忌讳。未议变通。窃以为过矣。朝廷者。礼法之所出。万民之所环视而效之者也。 殿下笃伦之德。虽不以临丧而有所加损。然过拘不足拘之忌。遂废不可废之礼。非所以示万民也。伏愿亟命有司。议临丧之礼于今日。幸甚。又伏念今廞卫将发。而留都百官。以出入时御之故。不得序班于郊外。将只望哭于政府忌讳。若此宁有穷已。亦乞许于郊外攀送。 答曰。临哭殡殿。情虽然矣。事势视昔有异。似难举行。拟于后日俗节。躬亲泄哀于魂殿耳。郊外祗送一款。当令该曹禀处焉。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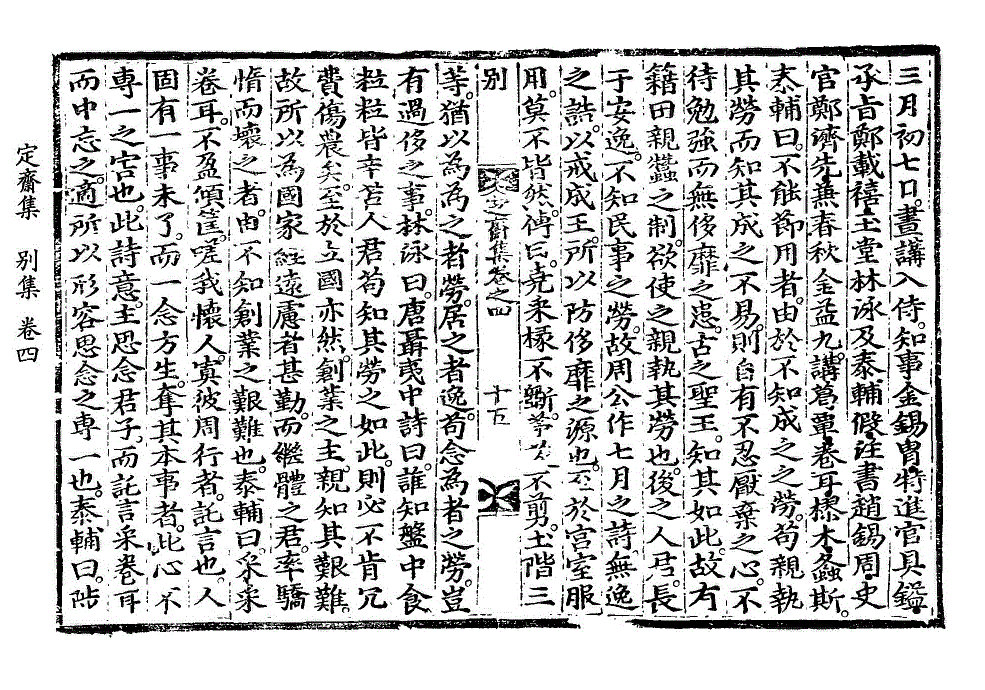 辛酉三月
辛酉三月初七日。昼讲入侍。知事金锡胄,特进官具镒,承旨郑载禧,玉堂林泳及泰辅,假注书赵锡周,史官郑济先,兼春秋金益九。讲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泰辅曰。不能节用者。由于不知成之之劳。苟亲执其劳而知其成之不易。则自有不忍厌弃之心。不待勉强而无侈靡之患。古之圣王。知其如此。故有籍田亲蚕之制。欲使之亲执其劳也。后之人君。长于安逸。不知民事之劳。故周公作七月之诗。无逸之诰。以戒成王。所以防侈靡之源也。至于宫室服用。莫不皆然。传曰。尧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阶三等。犹以为为之者劳。居之者逸。苟念为者之劳。岂有过侈之事。林泳曰。唐聂夷中诗曰。谁知盘中食。粒粒皆辛苦。人君苟知其劳之如此。则必不肯冗费伤农矣。至于立国亦然。创业之主。亲知其艰难。故所以为国家经远虑者甚勤。而继体之君。率骄惰而坏之者。由不知创业之艰难也。泰辅曰。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者。托言也。人固有一事未了。而一念方生。夺其本事者。此心不专一之害也。此诗意。主思念君子。而托言采卷耳而中忘之。适所以形容思念之专一也。泰辅曰。陟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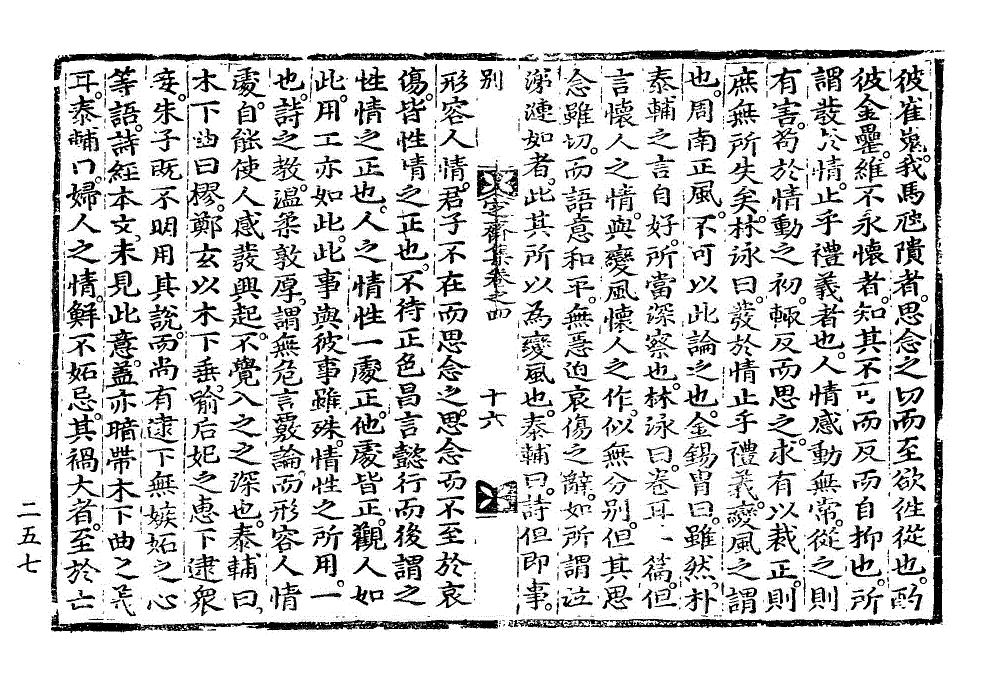 彼崔嵬。我马虺隤者。思念之切而至欲往从也。酌彼金罍。维不永怀者。知其不可而反而自抑也。所谓发于情。止乎礼义者也。人情感动无常。从之则有害。苟于情动之初。辄反而思之。求有以裁正。则庶无所失矣。林泳曰。发于情止乎礼义。变风之谓也。周南正风。不可以此论之也。金锡胄曰。虽然。朴泰辅之言自好。所当深察也。林泳曰。卷耳一篇。但言怀人之情。与变风怀人之作。似无分别。但其思念虽切。而语意和平。无急迫哀伤之辞。如所谓泣涕涟如者。此其所以为变风也。泰辅曰。诗但即事。形容人情。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思念而不至于哀伤。皆性情之正也。不待正色昌言懿行而后谓之性情之正也。人之情性一处正。他处皆正。观人如此。用工亦如此。此事与彼事虽殊。情性之所用。一也。诗之教。温柔敦厚。谓无危言覈论。而形容人情处。自能使人感发兴起。不觉入之之深也。泰辅曰。木下曲曰樛。郑玄以木下垂。喻后妃之惠下逮众妾。朱子既不明用其说。而尚有逮下无嫉妒之心等语。诗经本文。未见此意。盖亦暗带木下曲之义耳。泰辅曰。妇人之情。鲜不妒忌。其祸大者。至于亡
彼崔嵬。我马虺隤者。思念之切而至欲往从也。酌彼金罍。维不永怀者。知其不可而反而自抑也。所谓发于情。止乎礼义者也。人情感动无常。从之则有害。苟于情动之初。辄反而思之。求有以裁正。则庶无所失矣。林泳曰。发于情止乎礼义。变风之谓也。周南正风。不可以此论之也。金锡胄曰。虽然。朴泰辅之言自好。所当深察也。林泳曰。卷耳一篇。但言怀人之情。与变风怀人之作。似无分别。但其思念虽切。而语意和平。无急迫哀伤之辞。如所谓泣涕涟如者。此其所以为变风也。泰辅曰。诗但即事。形容人情。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思念而不至于哀伤。皆性情之正也。不待正色昌言懿行而后谓之性情之正也。人之情性一处正。他处皆正。观人如此。用工亦如此。此事与彼事虽殊。情性之所用。一也。诗之教。温柔敦厚。谓无危言覈论。而形容人情处。自能使人感发兴起。不觉入之之深也。泰辅曰。木下曲曰樛。郑玄以木下垂。喻后妃之惠下逮众妾。朱子既不明用其说。而尚有逮下无嫉妒之心等语。诗经本文。未见此意。盖亦暗带木下曲之义耳。泰辅曰。妇人之情。鲜不妒忌。其祸大者。至于亡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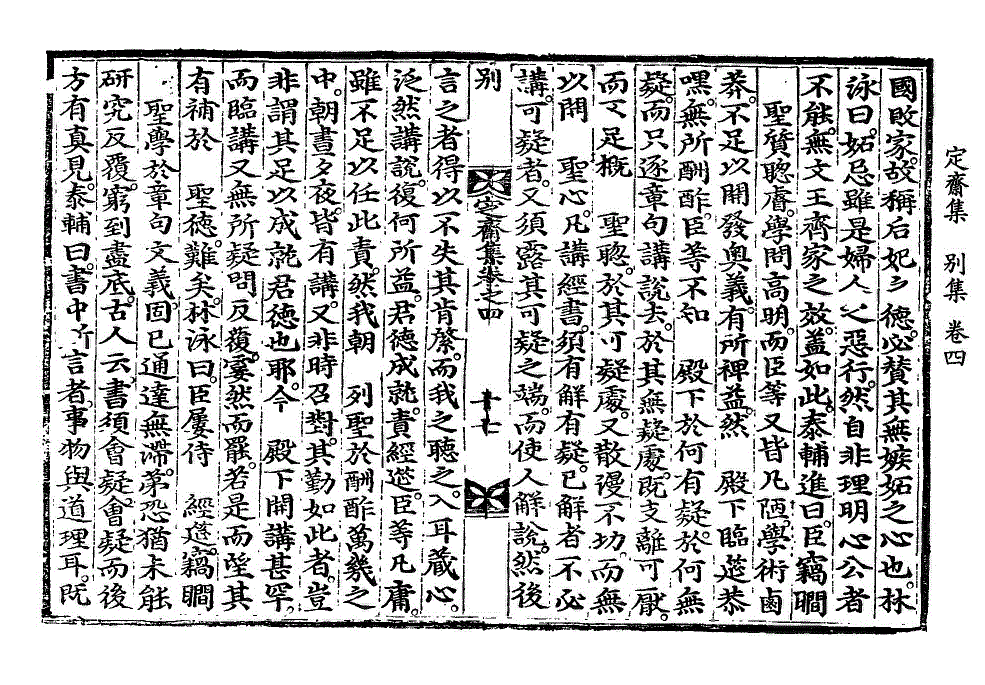 国败家。故称后妃之德。必赞其无嫉妒之心也。林泳曰。妒忌虽是妇人之恶行。然自非理明心公者不能。无文王齐家之效。盖如此。泰辅进曰。臣窃瞷 圣质聪睿。学问高明。而臣等又皆凡陋。学术卤莽。不足以开发奥义。有所裨益。然 殿下临筵恭嘿。无所酬酢。臣等不知 殿下于何有疑。于何无疑。而只逐章句讲说去。于其无疑处。既支离可厌。而不足概 圣聪。于其可疑处。又散漫不切。而无以开 圣心。凡讲经书。须有解有疑。已解者不必讲。可疑者。又须露其可疑之端。而使人解说。然后言之者得以不失其肯綮。而我之听之。入耳藏心。泛然讲说。复何所益。君德成就。责经筵。臣等凡庸。虽不足以任此责。然我朝 列圣于酬酢万几之中。朝昼夕夜。皆有讲。又非时召对。其勤如此者。岂非谓其足以成就君德也耶。今 殿下开讲甚罕。而临讲又无所疑问反覆。霎然而罢。若是而望其有补于 圣德。难矣。林泳曰。臣屡侍 经筵。窃瞷 圣学于章句文义。固已通达无滞。第恐犹未能研究反覆。穷到尽底。古人云。书须会疑。会疑而后方有真见。泰辅曰。书中所言者。事物与道理耳。既
国败家。故称后妃之德。必赞其无嫉妒之心也。林泳曰。妒忌虽是妇人之恶行。然自非理明心公者不能。无文王齐家之效。盖如此。泰辅进曰。臣窃瞷 圣质聪睿。学问高明。而臣等又皆凡陋。学术卤莽。不足以开发奥义。有所裨益。然 殿下临筵恭嘿。无所酬酢。臣等不知 殿下于何有疑。于何无疑。而只逐章句讲说去。于其无疑处。既支离可厌。而不足概 圣聪。于其可疑处。又散漫不切。而无以开 圣心。凡讲经书。须有解有疑。已解者不必讲。可疑者。又须露其可疑之端。而使人解说。然后言之者得以不失其肯綮。而我之听之。入耳藏心。泛然讲说。复何所益。君德成就。责经筵。臣等凡庸。虽不足以任此责。然我朝 列圣于酬酢万几之中。朝昼夕夜。皆有讲。又非时召对。其勤如此者。岂非谓其足以成就君德也耶。今 殿下开讲甚罕。而临讲又无所疑问反覆。霎然而罢。若是而望其有补于 圣德。难矣。林泳曰。臣屡侍 经筵。窃瞷 圣学于章句文义。固已通达无滞。第恐犹未能研究反覆。穷到尽底。古人云。书须会疑。会疑而后方有真见。泰辅曰。书中所言者。事物与道理耳。既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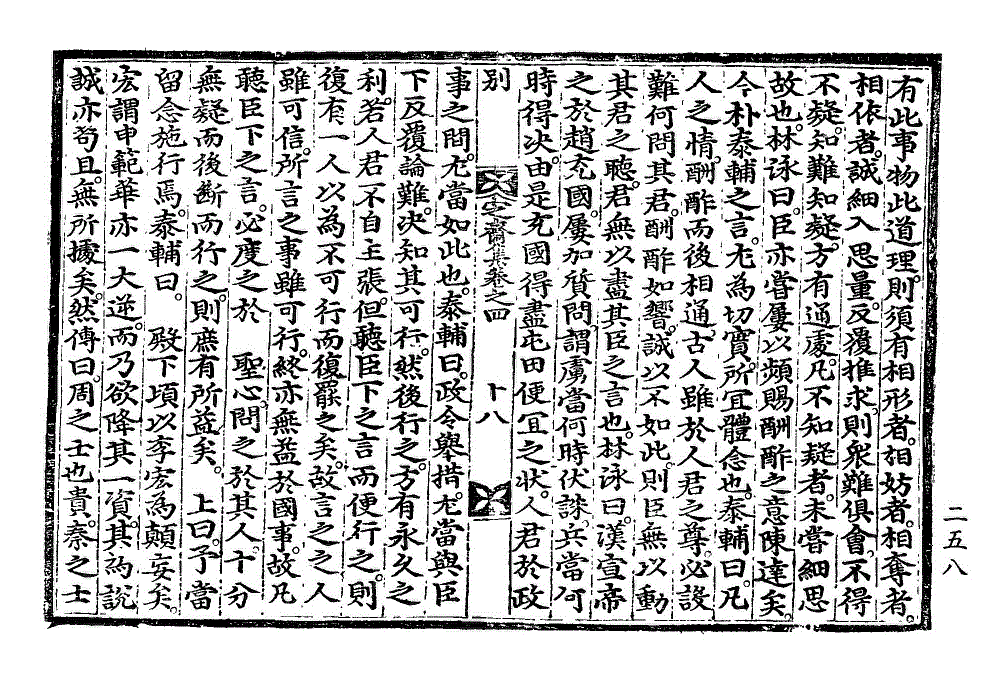 有此事物此道理。则须有相形者。相妨者。相夺者。相依者。诚细入思量。反覆推求。则众难俱会。不得不疑。知难知疑。方有通处。凡不知疑者。未尝细思故也。林泳曰。臣亦尝屡以频赐酬酢之意陈达矣。今朴泰辅之言。尤为切实。所宜体念也。泰辅曰。凡人之情。酬酢而后相通。古人虽于人君之尊。必设难何问其君。酬酢如响。诚以不如此。则臣无以动其君之听。君无以尽其臣之言也。林泳曰。汉宣帝之于赵充国。屡加质问。谓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由是充国得尽屯田便宜之状。人君于政事之间。尤当如此也。泰辅曰。政令举措。尤当与臣下反覆论难。决知其可行。然后行之。方有永久之利。若人君不自主张。但听臣下之言而便行之。则复有一人以为不可行而复罢之矣。故言之之人虽可信。所言之事虽可行。终亦无益于国事。故凡听臣下之言。必度之于 圣心。问之于其人。十分无疑而后断而行之。则庶有所益矣。 上曰。予当留念施行焉。泰辅曰。 殿下顷以李宏为颠妄矣。宏谓申范华亦一大逆。而乃欲降其一资。其为说诚亦苟且。无所据矣。然传曰。周之士也贵。秦之士
有此事物此道理。则须有相形者。相妨者。相夺者。相依者。诚细入思量。反覆推求。则众难俱会。不得不疑。知难知疑。方有通处。凡不知疑者。未尝细思故也。林泳曰。臣亦尝屡以频赐酬酢之意陈达矣。今朴泰辅之言。尤为切实。所宜体念也。泰辅曰。凡人之情。酬酢而后相通。古人虽于人君之尊。必设难何问其君。酬酢如响。诚以不如此。则臣无以动其君之听。君无以尽其臣之言也。林泳曰。汉宣帝之于赵充国。屡加质问。谓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由是充国得尽屯田便宜之状。人君于政事之间。尤当如此也。泰辅曰。政令举措。尤当与臣下反覆论难。决知其可行。然后行之。方有永久之利。若人君不自主张。但听臣下之言而便行之。则复有一人以为不可行而复罢之矣。故言之之人虽可信。所言之事虽可行。终亦无益于国事。故凡听臣下之言。必度之于 圣心。问之于其人。十分无疑而后断而行之。则庶有所益矣。 上曰。予当留念施行焉。泰辅曰。 殿下顷以李宏为颠妄矣。宏谓申范华亦一大逆。而乃欲降其一资。其为说诚亦苟且。无所据矣。然传曰。周之士也贵。秦之士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9H 页
 也贱。周之士。待之贵故自贵。秦之士。待之贱故自贱。朝廷者。多人之所会。故其言议酸咸辛苦。有万不同。若一不概于 圣心。而遽以颠妄等语摧折之。则不但有伤于容纳言者之道。亦无以砥砺士夫之廉节而使之自重也。臣窃惜之。此等辞气。望 殿下之留念省察焉。 上曰。申范华之有功。岂有不知。而纷纭提起。故略示未安之意尔。非为摧折也。然予亦当惕念省察焉。泰辅曰。 殿下于金锡胄疏。 批曰。宗社再安之功。实赖卿等效力之功。而未及一期如是陵轹。予实痛叹。以臣所见。未知其有所陵轹矣。且官师相规切。自是朝廷之美事。金锡胄在此矣。锡胄以 王室近戚。勋爵俱隆。亦锡胄小心戒慎之日也。况国家倚重之人。尤当不厌相规。是以诸葛亮之言曰。诸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若谓此人功劳如此其盛尔。何敢陵轹。则不但非朝廷之美事。亦恐非锡胄之所愿也。 上曰。追录之后。人多不信。纷纭起闹于已久之后。故于元勋疏批。略示予意矣。金锡胄曰。心经者。圣贤心法之要。曾在 先王朝。宋浚吉进讲心经。时臣与朴泰辅之父世堂。俱以玉堂同侍。听浚
也贱。周之士。待之贵故自贵。秦之士。待之贱故自贱。朝廷者。多人之所会。故其言议酸咸辛苦。有万不同。若一不概于 圣心。而遽以颠妄等语摧折之。则不但有伤于容纳言者之道。亦无以砥砺士夫之廉节而使之自重也。臣窃惜之。此等辞气。望 殿下之留念省察焉。 上曰。申范华之有功。岂有不知。而纷纭提起。故略示未安之意尔。非为摧折也。然予亦当惕念省察焉。泰辅曰。 殿下于金锡胄疏。 批曰。宗社再安之功。实赖卿等效力之功。而未及一期如是陵轹。予实痛叹。以臣所见。未知其有所陵轹矣。且官师相规切。自是朝廷之美事。金锡胄在此矣。锡胄以 王室近戚。勋爵俱隆。亦锡胄小心戒慎之日也。况国家倚重之人。尤当不厌相规。是以诸葛亮之言曰。诸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若谓此人功劳如此其盛尔。何敢陵轹。则不但非朝廷之美事。亦恐非锡胄之所愿也。 上曰。追录之后。人多不信。纷纭起闹于已久之后。故于元勋疏批。略示予意矣。金锡胄曰。心经者。圣贤心法之要。曾在 先王朝。宋浚吉进讲心经。时臣与朴泰辅之父世堂。俱以玉堂同侍。听浚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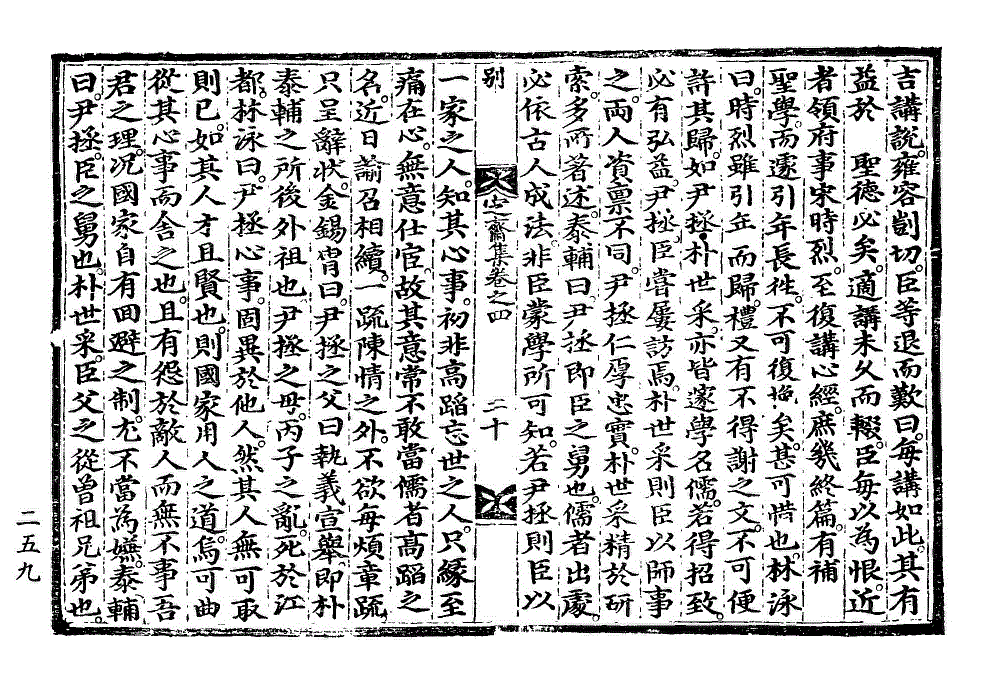 吉讲说。雍容剀切。臣等退而叹曰。每讲如此。其有益于 圣德必矣。适讲未久而辍。臣每以为恨。近者领府事宋时烈。至复讲心经。庶几终篇。有补 圣学。而遽引年长往。不可复挽矣。甚可惜也。林泳曰。时烈虽引年而归。礼又有不得谢之文。不可便许其归。如尹拯,朴世采。亦皆邃学名儒。若得招致。必有弘益。尹拯。臣尝屡访焉。朴世采则臣以师事之。两人资禀不同。尹拯仁厚忠实。朴世采精于研索。多所著述。泰辅曰。尹拯即臣之舅也。儒者出处。必依古人成法。非臣蒙学所可知。若尹拯则臣以一家之人。知其心事。初非高蹈忘世之人。只缘至痛在心。无意仕宦。故其意常不敢当儒者高蹈之名。近日谕召相续。一疏陈情之外。不欲每烦章疏。只呈辞状。金锡胄曰。尹拯之父曰执义宣举。即朴泰辅之所后外祖也。尹拯之母。丙子之乱。死于江都。林泳曰。尹拯心事。固异于他人。然其人无可取则已。如其人才且贤也。则国家用人之道。乌可曲从其心事而舍之也。且有怨于敌人而无不事吾君之理。况国家自有回避之制。尤不当为嫌。泰辅曰。尹拯。臣之舅也。朴世采。臣父之从曾祖兄弟也。
吉讲说。雍容剀切。臣等退而叹曰。每讲如此。其有益于 圣德必矣。适讲未久而辍。臣每以为恨。近者领府事宋时烈。至复讲心经。庶几终篇。有补 圣学。而遽引年长往。不可复挽矣。甚可惜也。林泳曰。时烈虽引年而归。礼又有不得谢之文。不可便许其归。如尹拯,朴世采。亦皆邃学名儒。若得招致。必有弘益。尹拯。臣尝屡访焉。朴世采则臣以师事之。两人资禀不同。尹拯仁厚忠实。朴世采精于研索。多所著述。泰辅曰。尹拯即臣之舅也。儒者出处。必依古人成法。非臣蒙学所可知。若尹拯则臣以一家之人。知其心事。初非高蹈忘世之人。只缘至痛在心。无意仕宦。故其意常不敢当儒者高蹈之名。近日谕召相续。一疏陈情之外。不欲每烦章疏。只呈辞状。金锡胄曰。尹拯之父曰执义宣举。即朴泰辅之所后外祖也。尹拯之母。丙子之乱。死于江都。林泳曰。尹拯心事。固异于他人。然其人无可取则已。如其人才且贤也。则国家用人之道。乌可曲从其心事而舍之也。且有怨于敌人而无不事吾君之理。况国家自有回避之制。尤不当为嫌。泰辅曰。尹拯。臣之舅也。朴世采。臣父之从曾祖兄弟也。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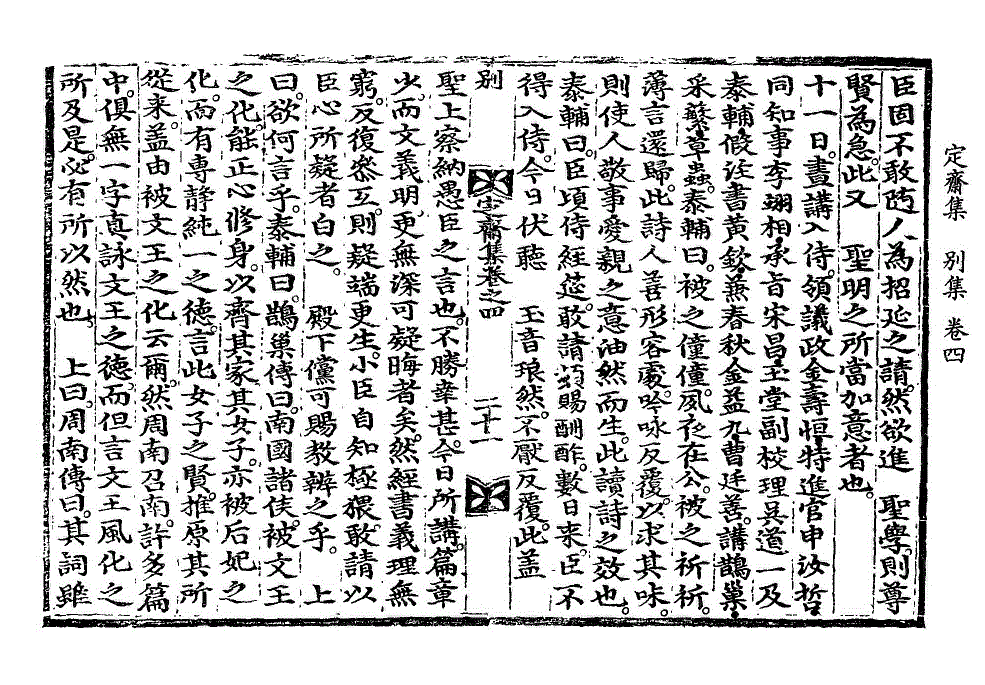 臣固不敢随人为招延之请。然欲进 圣学。则尊贤为急。此又 圣明之所当加意者也。
臣固不敢随人为招延之请。然欲进 圣学。则尊贤为急。此又 圣明之所当加意者也。十一日。昼讲入侍。领议政金寿恒,特进官申汝哲,同知事李翊相,承旨宋昌,玉堂副校理吴道一及泰辅,假注书黄钦,兼春秋金益九,曹廷善。讲鹊巢,采蘩,草虫。泰辅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言还归。此诗人善形容处。吟咏反覆。以求其味。则使人敬事爱亲之意油然而生。此读诗之效也。泰辅曰。臣顷侍经筵。敢请频赐酬酢。数日来。臣不得入侍。今日伏听 玉音琅然。不厌反覆。此盖 圣上察纳愚臣之言也。不胜幸甚。今日所讲。篇章少。而文义明。更无深可疑晦者矣。然经书义理无穷。反复参互。则疑端更生。小臣自知极猥。敢请以臣心所疑者白之。 殿下傥可赐教辨之乎。 上曰。欲何言乎。泰辅曰。鹊巢传曰。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言此女子之贤。推原其所从来。盖由被文王之化云尔。然周南召南。许多篇中。俱无一字真咏文王之德。而但言文王风化之所及是。必有所以然也。 上曰。周南传曰。其词虽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0L 页
 主于后妃。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误矣。故虽不言文王。文王之德自著矣。泰辅曰。 上教则然矣。然周南召南者。风也。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之相与咏歌者也。里巷之人。遇事即物。各言其情。初未尝有以此著明文王教化之意。采诗者。即诗而求其人之性情。即其人性情之正。知其由于文王之教化。如此篇。观女子之贤。则知其被后妃之化。又足以知其诸侯之能修身齐家。诸侯之贤。后妃之化。皆本于文王之教。此乃溯而源之。推而极之而知其所本也。非诗人元有赞咏文王之意。是故周南召南。无咏文王之德者。而文王之德则咏于雅颂。雅颂者。朝廷之乐故也。故于二南。知文王之教所被之远。于雅颂。知文王之德所存之盛。泰辅进曰。献纳为亚长阶梯。为任重。献纳李纶。迟钝且不晓事。顷者司谏赵持谦。以诸译并鞫之论引避也。纶避辞曰。诸译并鞫。果当于狱情。则何敢自以为是而处置持谦乎。既不立所见。又不自引咎。其无主见如此。且台谏。疏陈所怀。非辞职。则自当连启。昨纶以陈疏之故。无端
主于后妃。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误矣。故虽不言文王。文王之德自著矣。泰辅曰。 上教则然矣。然周南召南者。风也。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之相与咏歌者也。里巷之人。遇事即物。各言其情。初未尝有以此著明文王教化之意。采诗者。即诗而求其人之性情。即其人性情之正。知其由于文王之教化。如此篇。观女子之贤。则知其被后妃之化。又足以知其诸侯之能修身齐家。诸侯之贤。后妃之化。皆本于文王之教。此乃溯而源之。推而极之而知其所本也。非诗人元有赞咏文王之意。是故周南召南。无咏文王之德者。而文王之德则咏于雅颂。雅颂者。朝廷之乐故也。故于二南。知文王之教所被之远。于雅颂。知文王之德所存之盛。泰辅进曰。献纳为亚长阶梯。为任重。献纳李纶。迟钝且不晓事。顷者司谏赵持谦。以诸译并鞫之论引避也。纶避辞曰。诸译并鞫。果当于狱情。则何敢自以为是而处置持谦乎。既不立所见。又不自引咎。其无主见如此。且台谏。疏陈所怀。非辞职。则自当连启。昨纶以陈疏之故。无端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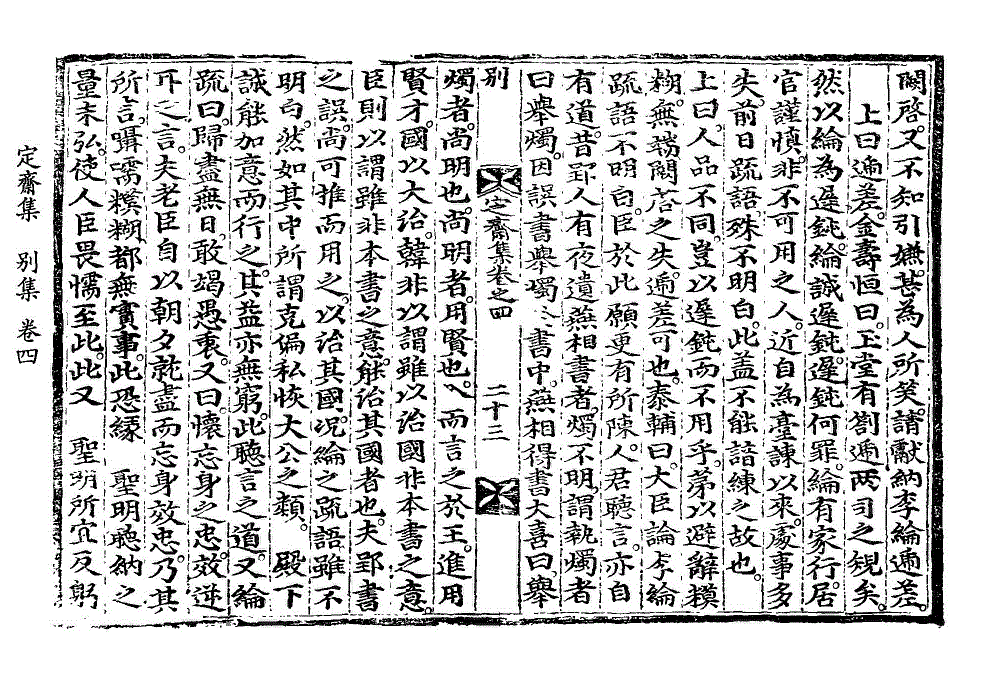 阙启。又不知引嫌。甚为人所笑。请献纳李纶递差。 上曰递差。金寿恒曰。玉堂有劄递两司之规矣。然以纶为迟钝。纶诚迟钝。迟钝何罪。纶有家行。居官谨慎。非不可用之人。近自为台谏以来。处事多失。前日疏语。殊不明白。此盖不能谙练之故也。 上曰。人品不同。岂以迟钝而不用乎。第以避辞模糊。无端阙启之失。递差可也。泰辅曰。大臣论李纶疏语不明白。臣于此愿更有所陈。人君听言。亦自有道。昔郢人有夜遗燕相书者。烛不明。谓执烛者曰举烛。因误书举烛于书中。燕相得书大喜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用贤也。入而言之于王。进用贤才。国以大治。韩非以谓虽以治国非本书之意。臣则以谓虽非本书之意。能治其国者也。夫郢书之误。尚可推而用之。以治其国。况纶之疏语。虽不明白。然如其中所谓克偏私恢大公之类。 殿下诚能加意而行之。其益亦无穷。此听言之道。又纶疏曰。归尽无日。敢竭愚衷。又曰。怀忘身之忠。效逆耳之言。夫老臣自以朝夕就尽而忘身效忠。乃其所言。嗫嚅模糊。都无实事。此恐缘 圣明听纳之量未弘。使人臣畏懦至此。此又 圣明所宜反躬
阙启。又不知引嫌。甚为人所笑。请献纳李纶递差。 上曰递差。金寿恒曰。玉堂有劄递两司之规矣。然以纶为迟钝。纶诚迟钝。迟钝何罪。纶有家行。居官谨慎。非不可用之人。近自为台谏以来。处事多失。前日疏语。殊不明白。此盖不能谙练之故也。 上曰。人品不同。岂以迟钝而不用乎。第以避辞模糊。无端阙启之失。递差可也。泰辅曰。大臣论李纶疏语不明白。臣于此愿更有所陈。人君听言。亦自有道。昔郢人有夜遗燕相书者。烛不明。谓执烛者曰举烛。因误书举烛于书中。燕相得书大喜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用贤也。入而言之于王。进用贤才。国以大治。韩非以谓虽以治国非本书之意。臣则以谓虽非本书之意。能治其国者也。夫郢书之误。尚可推而用之。以治其国。况纶之疏语。虽不明白。然如其中所谓克偏私恢大公之类。 殿下诚能加意而行之。其益亦无穷。此听言之道。又纶疏曰。归尽无日。敢竭愚衷。又曰。怀忘身之忠。效逆耳之言。夫老臣自以朝夕就尽而忘身效忠。乃其所言。嗫嚅模糊。都无实事。此恐缘 圣明听纳之量未弘。使人臣畏懦至此。此又 圣明所宜反躬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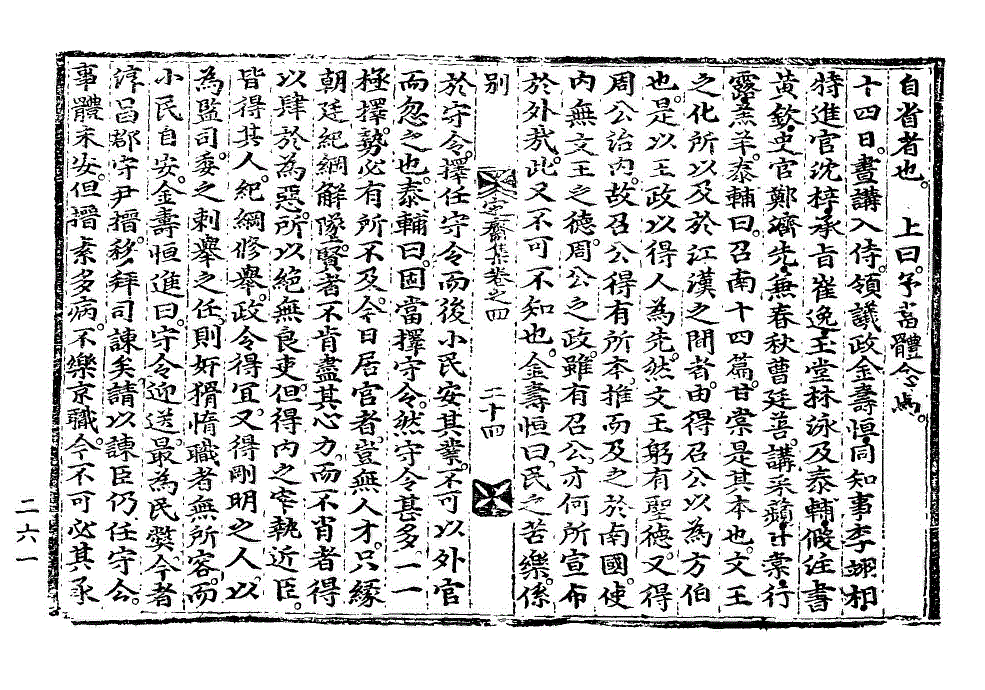 自省者也。 上曰。予当体念焉。
自省者也。 上曰。予当体念焉。十四日。昼讲入侍。领议政金寿恒,同知事李翊相,特进官沈梓,承旨崔逸,玉堂林泳及泰辅,假注书黄钦,史官郑济先,兼春秋曹廷善。讲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泰辅曰。召南十四篇。甘棠是其本也。文王之化所以及于江汉之间者。由得召公以为方伯也。是以王政以得人为先。然文王躬有圣德。又得周公治内。故召公得有所本。推而及之于南国。使内无文王之德。周公之政。虽有召公。亦何所宣布于外哉。此又不可不知也。金寿恒曰。民之苦乐。系于守令。择任守令而后小民安其业。不可以外官而忽之也。泰辅曰。固当择守令。然守令甚多。一一极择。势必有所不及。今日居官者。岂无人才。只缘朝廷纪纲解坠。贤者不肯尽其心力。而不肖者得以肆于为恶。所以绝无良吏。但得内之宰执近臣。皆得其人。纪纲修举。政令得宜。又得刚明之人。以为监司。委之刺举之任。则奸猾惰职者无所容。而小民自安。金寿恒进曰。守令迎送。最为民弊。今者淳昌郡守尹搢。移拜司谏矣。请以谏臣仍任守令。事体未安。但搢素多病。不乐京职。今不可必其承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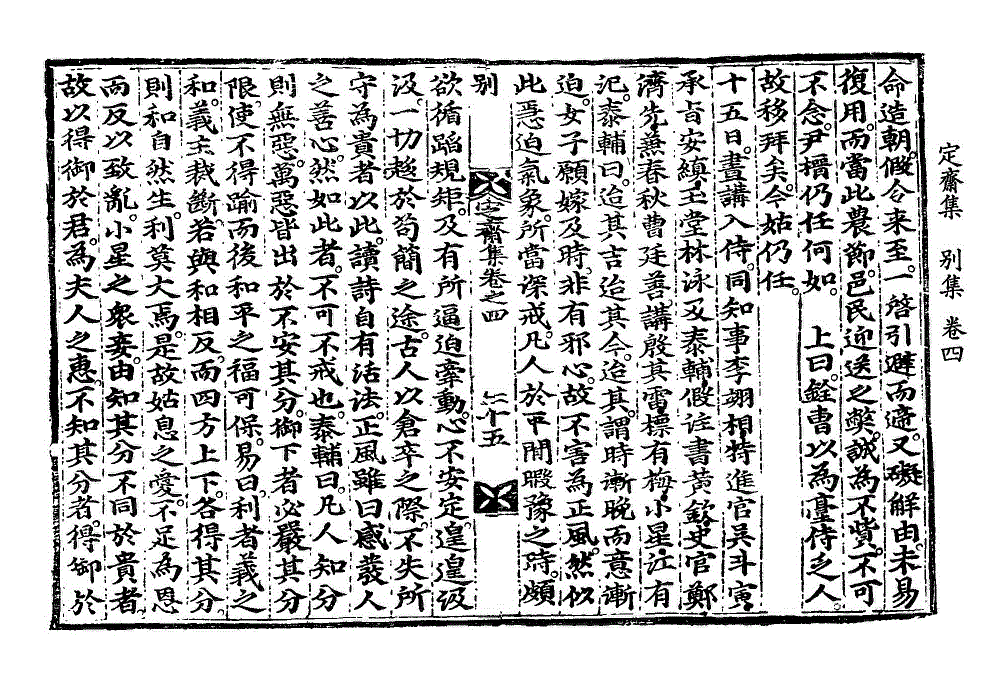 命造朝。假令来至。一启引避而遆。又碍解由。未易复用。而当此农节。邑民迎送之弊。诚为不赀。不可不念。尹搢仍任何如。 上曰。铨曹以为台侍乏人。故移拜矣。今姑仍任。
命造朝。假令来至。一启引避而遆。又碍解由。未易复用。而当此农节。邑民迎送之弊。诚为不赀。不可不念。尹搢仍任何如。 上曰。铨曹以为台侍乏人。故移拜矣。今姑仍任。十五日。昼讲入侍。同知事李翊相,特进官吴斗寅,承旨安缜,玉堂林泳及泰辅,假注书黄钦,史官郑济先,兼春秋曹廷善。讲殷其雷,标有梅,小星,江有汜。泰辅曰。迨其吉迨其今。迨其。谓时渐晚而意渐迫。女子愿嫁及时。非有邪心。故不害为正风。然似此急迫气象。所当深戒。凡人于平閒暇豫之时。颇欲循蹈规矩。及有所逼迫牵动。心不安定。遑遑汲汲。一切趍于苟简之途。古人以仓卒之际。不失所守为贵者以此。读诗自有活法。正风虽曰感发人之善心。然如此者。不可不戒也。泰辅曰。凡人知分则无恶。万恶皆出于不安其分。御下者必严其分限。使不得踰而后和平之福可保。易曰。利者义之和。义主裁断。若与和相反。而四方上下。各得其分。则和自然生。利莫大焉。是故姑息之爱。不足为恩而反以致乱。小星之众妾。由知其分不同于贵者。故以得御于君。为夫人之惠。不知其分者。得御于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2L 页
 君。则反嫉夫人。不但妃妾为然。御下者。所不可不知也。林泳曰。诸葛亮所谓法行而知恩者此也。泰辅曰。悔之于人甚大。易有吉凶悔吝。吉凶对立。而悔为由凶趍吉之道路。转移之机。亶在于悔。以江有汜论之。未悔之前。不我以。其私邪褊迫。为如何哉。既悔之后。能处能歌。其公正愉快。为如何哉。当其方悔之时。系着羞涩之意。牵于后。明断奋决之意。动于前。其交战胜负之机。又可以想见也。一朝舍旧图新。但见其公正愉快。而向来私邪褊迫之累。果安在哉。悔之于人。其大如此。而人尚文过护非而不忍变。岂不哀哉。以此一篇。讽咏上下。可以得之矣。泳,泰辅同进曰。近日台谏褫代如邮驿。国朝故事。有一人为大司宪九年者。今满一月者。甚罕或朝拜而夕改。由是台谏事体甚轻。昨日大臣请仍任司谏尹搢。事体极未安。但以今日事势言之。司谏为朝夕褫代之官。而农节迎送之弊甚钜。所重反有在于彼。故不得已为此请也。如近日承旨宋昌论金化县监申晔移拜持平。迎送有弊。都承旨洪万容请变通在外台臣金灏等。得递差之命。皆大伤事体。台臣之任甚重。有以一人之进退。
君。则反嫉夫人。不但妃妾为然。御下者。所不可不知也。林泳曰。诸葛亮所谓法行而知恩者此也。泰辅曰。悔之于人甚大。易有吉凶悔吝。吉凶对立。而悔为由凶趍吉之道路。转移之机。亶在于悔。以江有汜论之。未悔之前。不我以。其私邪褊迫。为如何哉。既悔之后。能处能歌。其公正愉快。为如何哉。当其方悔之时。系着羞涩之意。牵于后。明断奋决之意。动于前。其交战胜负之机。又可以想见也。一朝舍旧图新。但见其公正愉快。而向来私邪褊迫之累。果安在哉。悔之于人。其大如此。而人尚文过护非而不忍变。岂不哀哉。以此一篇。讽咏上下。可以得之矣。泳,泰辅同进曰。近日台谏褫代如邮驿。国朝故事。有一人为大司宪九年者。今满一月者。甚罕或朝拜而夕改。由是台谏事体甚轻。昨日大臣请仍任司谏尹搢。事体极未安。但以今日事势言之。司谏为朝夕褫代之官。而农节迎送之弊甚钜。所重反有在于彼。故不得已为此请也。如近日承旨宋昌论金化县监申晔移拜持平。迎送有弊。都承旨洪万容请变通在外台臣金灏等。得递差之命。皆大伤事体。台臣之任甚重。有以一人之进退。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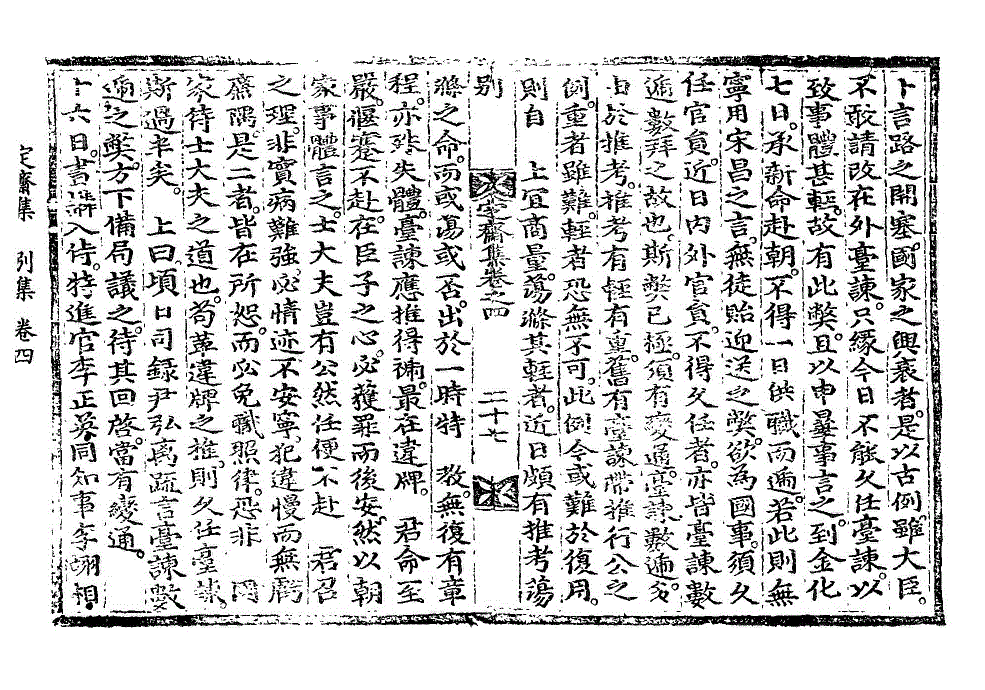 卜言路之开塞。国家之兴衰者。是以古例。虽大臣。不敢请改在外台谏。只缘今日不能久任台谏。以致事体甚轻。故有此弊。且以申晔事言之。到金化七日。承新命赴朝。不得一日供职而递。若此则无宁用宋昌之言。无徒贻迎送之弊。欲为国事。须久任官员。近日内外官员。不得久任者。亦皆台谏数递数拜之故也。斯弊已极。须有变通。台谏数递。多由于推考。推考有轻有重。旧有台谏带推行公之例。重者虽难。轻者恐无不可。此例今或难于复用。则自 上宜商量。荡涤其轻者。近日颇有推考荡涤之命。而或荡或否。出于一时特 教。无复有章程。亦殊失体。台谏应推得褫。最在违牌。 君命至严。偃蹇不赴。在臣子之心。必获罪而后安。然以朝家事体言之。士大夫岂有公然任便不赴 君召之理。非实病难强。必情迹不安宁。犯违慢而无亏廉隅。是二者。皆在所恕。而必免职照律。恐非 国家待士大夫之道也。苟革违牌之推。则久任台谏。斯过半矣。 上曰。顷日司录尹弘离疏言台谏数递之弊。方下备局议之。待其回启。当有变通。
卜言路之开塞。国家之兴衰者。是以古例。虽大臣。不敢请改在外台谏。只缘今日不能久任台谏。以致事体甚轻。故有此弊。且以申晔事言之。到金化七日。承新命赴朝。不得一日供职而递。若此则无宁用宋昌之言。无徒贻迎送之弊。欲为国事。须久任官员。近日内外官员。不得久任者。亦皆台谏数递数拜之故也。斯弊已极。须有变通。台谏数递。多由于推考。推考有轻有重。旧有台谏带推行公之例。重者虽难。轻者恐无不可。此例今或难于复用。则自 上宜商量。荡涤其轻者。近日颇有推考荡涤之命。而或荡或否。出于一时特 教。无复有章程。亦殊失体。台谏应推得褫。最在违牌。 君命至严。偃蹇不赴。在臣子之心。必获罪而后安。然以朝家事体言之。士大夫岂有公然任便不赴 君召之理。非实病难强。必情迹不安宁。犯违慢而无亏廉隅。是二者。皆在所恕。而必免职照律。恐非 国家待士大夫之道也。苟革违牌之推。则久任台谏。斯过半矣。 上曰。顷日司录尹弘离疏言台谏数递之弊。方下备局议之。待其回启。当有变通。十六日。昼讲入侍。特进官李正英,同知事李翊相,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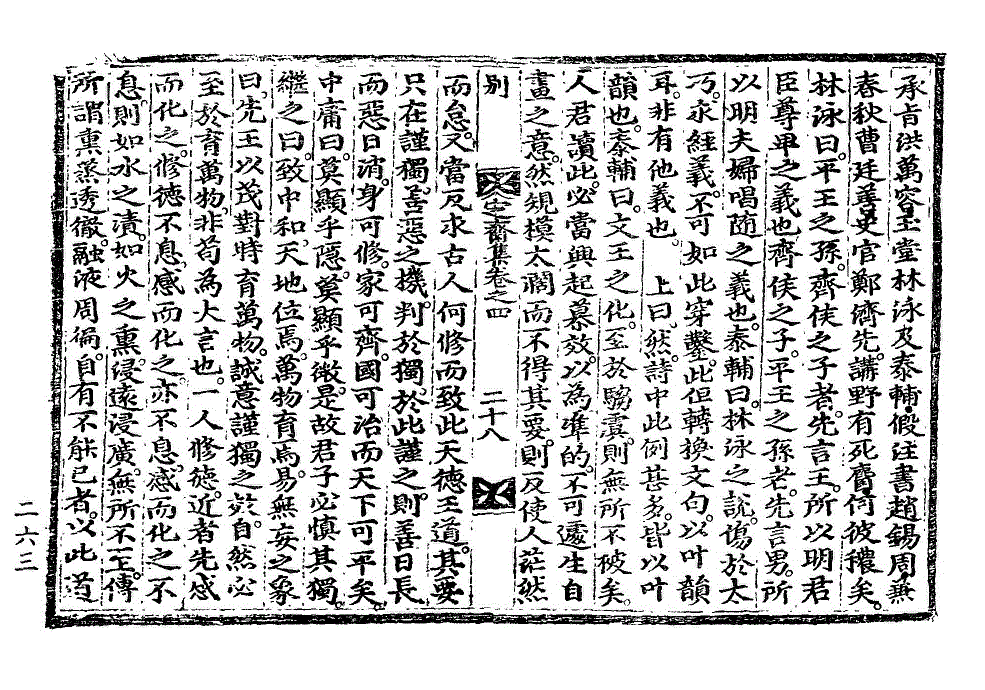 承旨洪万容,玉堂林泳及泰辅,假注书赵锡周,兼春秋曹廷善,史官郑济先。讲野有死麇,何彼秾矣。林泳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者。先言王。所以明君臣尊卑之义也。齐侯之子。平王之孙者。先言男。所以明夫妇唱随之义也。泰辅曰。林泳之说。伤于太巧。求经义。不可如此穿凿。此但转换文句。以叶韵耳。非有他义也。 上曰。然。诗中此例甚多。皆以叶韵也。泰辅曰。文王之化。至于驺虞。则无所不被矣。人君读此。必当兴起慕效。以为准的。不可遽生自画之意。然规模太阔而不得其要。则反使人茫然而怠。又当反求古人何修而致此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谨独。善恶之机。判于独。于此谨之。则善日长而恶日消。身可修。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中庸曰。莫显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必慎其独。继之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诚意谨独之效。自然必至于育万物。非苟为大言也。一人修德。近者先感而化之。修德不息。感而化之。亦不息。感而化之不息。则如水之渍。如火之熏。浸远浸广。无所不至。传所谓熏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以此道
承旨洪万容,玉堂林泳及泰辅,假注书赵锡周,兼春秋曹廷善,史官郑济先。讲野有死麇,何彼秾矣。林泳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者。先言王。所以明君臣尊卑之义也。齐侯之子。平王之孙者。先言男。所以明夫妇唱随之义也。泰辅曰。林泳之说。伤于太巧。求经义。不可如此穿凿。此但转换文句。以叶韵耳。非有他义也。 上曰。然。诗中此例甚多。皆以叶韵也。泰辅曰。文王之化。至于驺虞。则无所不被矣。人君读此。必当兴起慕效。以为准的。不可遽生自画之意。然规模太阔而不得其要。则反使人茫然而怠。又当反求古人何修而致此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谨独。善恶之机。判于独。于此谨之。则善日长而恶日消。身可修。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中庸曰。莫显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必慎其独。继之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诚意谨独之效。自然必至于育万物。非苟为大言也。一人修德。近者先感而化之。修德不息。感而化之。亦不息。感而化之不息。则如水之渍。如火之熏。浸远浸广。无所不至。传所谓熏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以此道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4H 页
 也。如或时作时止。不能不息。则气脉间断。何能远及。周敦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故苟失其要。劳而无成。苟得其要。约而能广。林泳进曰。诗传旧多合周召南为一册。今进讲者。并邶为一册。一册毕。例当温绎。今日毕讲二南。二南者。正风意味最长。虽未毕册。谓宜别为温绎。 上曰。然。此册不同于旧。其令改妆。泰辅曰。林泳别请温绎二南者。其意不偶。 殿下在宫中温绎节度。臣等不得与知。未知工夫果如何。必须反覆玩味。真得所谓读了二南。便不面墙者。然后方有温绎之益矣。林泳复进曰。二南备陈文王正家之教。所以为端本出治之源也。今大礼有期。而适讲二南。伏愿深加玩索。体之于身。以正风化之始。又曰。臣初入讲筵。已尝以立志之说仰陈矣。其后侍讲已久。尚未知 殿下立志如何。 殿下见古人事业。以为予亦当如是乎。抑以为高远而不可及乎。臣诚惶恐。敢请闻之。 上曰。予见古人事业。未尝以为高远而不可及。亦常有有为若是之心。林泳曰。宋神宗。近代以来。最号英明。程颢尝论王道。神宗曰。此尧舜
也。如或时作时止。不能不息。则气脉间断。何能远及。周敦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故苟失其要。劳而无成。苟得其要。约而能广。林泳进曰。诗传旧多合周召南为一册。今进讲者。并邶为一册。一册毕。例当温绎。今日毕讲二南。二南者。正风意味最长。虽未毕册。谓宜别为温绎。 上曰。然。此册不同于旧。其令改妆。泰辅曰。林泳别请温绎二南者。其意不偶。 殿下在宫中温绎节度。臣等不得与知。未知工夫果如何。必须反覆玩味。真得所谓读了二南。便不面墙者。然后方有温绎之益矣。林泳复进曰。二南备陈文王正家之教。所以为端本出治之源也。今大礼有期。而适讲二南。伏愿深加玩索。体之于身。以正风化之始。又曰。臣初入讲筵。已尝以立志之说仰陈矣。其后侍讲已久。尚未知 殿下立志如何。 殿下见古人事业。以为予亦当如是乎。抑以为高远而不可及乎。臣诚惶恐。敢请闻之。 上曰。予见古人事业。未尝以为高远而不可及。亦常有有为若是之心。林泳曰。宋神宗。近代以来。最号英明。程颢尝论王道。神宗曰。此尧舜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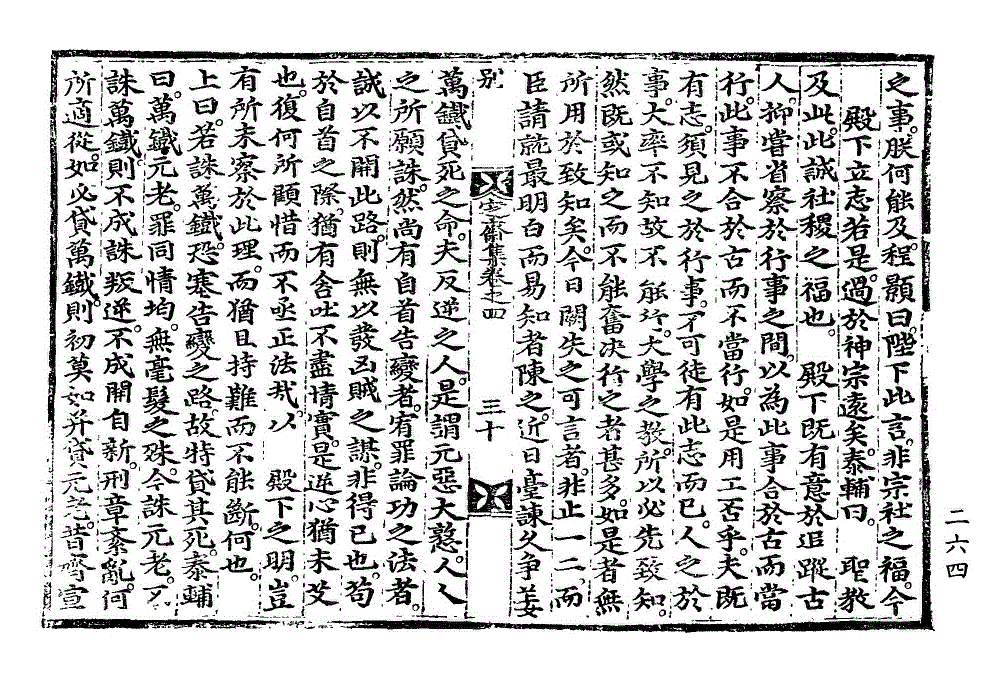 之事。朕何能及。程颢曰。陛下此言。非宗社之福。今 殿下立志若是。过于神宗远矣。泰辅曰。 圣教及此。此诚社稷之福也。 殿下既有意于追踪古人。抑尝省察于行事之间。以为此事合于古而当行。此事不合于古而不当行。如是用工否乎。夫既有志。须见之于行事。不可徒有此志而已。人之于事。大率不知故不能行。大学之教。所以必先致知。然既或知之而不能奋决行之者甚多。如是者无所用于致知矣。今日阙失之可言者。非止一二。而臣请就最明白而易知者陈之。近日台谏久争姜万铁贷死之命。夫反逆之人。是谓元恶大憝。人人之所愿诛。然尚有自首告变者。宥罪论功之法者。诚以不开此路。则无以发凶贼之谋。非得已也。苟于自首之际。犹有含吐不尽情实。是逆心犹未艾也。复何所顾惜而不亟正法哉。以 殿下之明。岂有所未察于此理。而犹且持难而不能断。何也。 上曰。若诛万铁。恐塞告变之路。故特贷其死。泰辅曰。万铁,元老。罪同情均。无毫发之殊。今诛元老。不诛万铁。则不成诛叛逆。不成开自新。刑章紊乱。何所适从。如必贷万铁。则初莫如并贷元老。昔齐宣
之事。朕何能及。程颢曰。陛下此言。非宗社之福。今 殿下立志若是。过于神宗远矣。泰辅曰。 圣教及此。此诚社稷之福也。 殿下既有意于追踪古人。抑尝省察于行事之间。以为此事合于古而当行。此事不合于古而不当行。如是用工否乎。夫既有志。须见之于行事。不可徒有此志而已。人之于事。大率不知故不能行。大学之教。所以必先致知。然既或知之而不能奋决行之者甚多。如是者无所用于致知矣。今日阙失之可言者。非止一二。而臣请就最明白而易知者陈之。近日台谏久争姜万铁贷死之命。夫反逆之人。是谓元恶大憝。人人之所愿诛。然尚有自首告变者。宥罪论功之法者。诚以不开此路。则无以发凶贼之谋。非得已也。苟于自首之际。犹有含吐不尽情实。是逆心犹未艾也。复何所顾惜而不亟正法哉。以 殿下之明。岂有所未察于此理。而犹且持难而不能断。何也。 上曰。若诛万铁。恐塞告变之路。故特贷其死。泰辅曰。万铁,元老。罪同情均。无毫发之殊。今诛元老。不诛万铁。则不成诛叛逆。不成开自新。刑章紊乱。何所适从。如必贷万铁。则初莫如并贷元老。昔齐宣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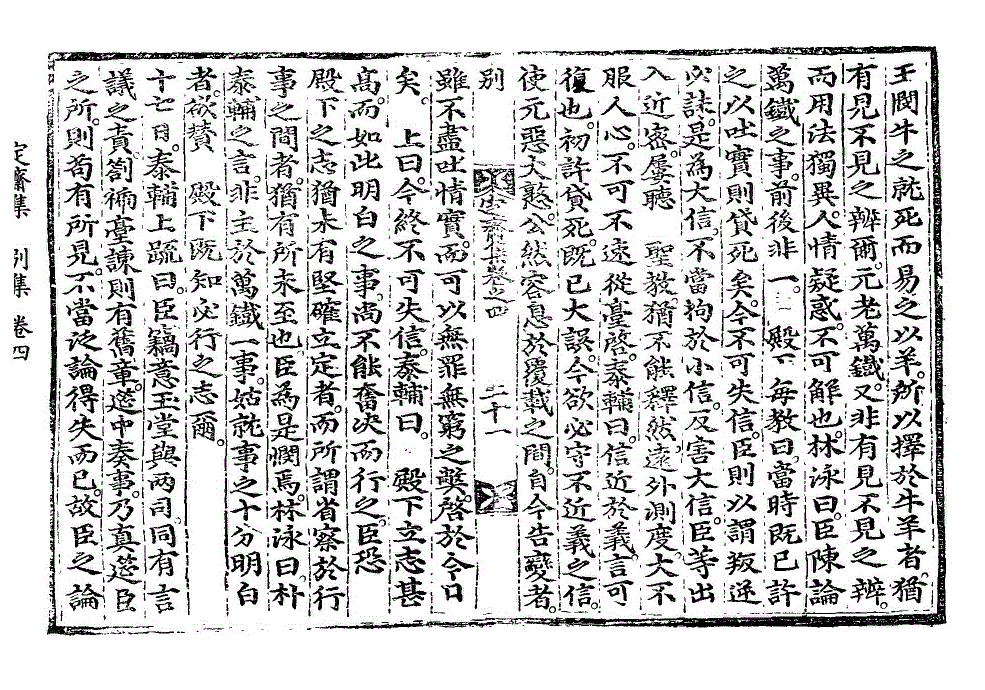 王悯牛之就死而易之以羊。所以择于牛羊者。犹有见不见之辨尔。元老万铁。又非有见不见之辨。而用法独异。人情疑惑。不可解也。林泳曰。臣陈论万铁之事。前后非一。 殿下每教曰。当时既已许之以吐实则贷死矣。今不可失信。臣则以谓叛逆必诛。是为大信。不当拘于小信。反害大信。臣等出入近密。屡听 圣教。犹不能释然。远外测度。大不服人心。不可不速从台启。泰辅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初许贷死。既已大误。今欲必守不近义之信。使元恶大憝。公然容息于覆载之间。自今告变者。虽不尽吐情实。而可以无罪无穷之弊。启于今日矣。 上曰。今终不可失信。泰辅曰。 殿下立志甚高。而如此明白之事。尚不能奋决而行之。臣恐 殿下之志犹未有坚确立定者。而所谓省察于行事之间者。犹有所未至也。臣为是悯焉。林泳曰。朴泰辅之言。非主于万铁一事。姑就事之十分明白者。欲赞 殿下既知必行之志尔。
王悯牛之就死而易之以羊。所以择于牛羊者。犹有见不见之辨尔。元老万铁。又非有见不见之辨。而用法独异。人情疑惑。不可解也。林泳曰。臣陈论万铁之事。前后非一。 殿下每教曰。当时既已许之以吐实则贷死矣。今不可失信。臣则以谓叛逆必诛。是为大信。不当拘于小信。反害大信。臣等出入近密。屡听 圣教。犹不能释然。远外测度。大不服人心。不可不速从台启。泰辅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初许贷死。既已大误。今欲必守不近义之信。使元恶大憝。公然容息于覆载之间。自今告变者。虽不尽吐情实。而可以无罪无穷之弊。启于今日矣。 上曰。今终不可失信。泰辅曰。 殿下立志甚高。而如此明白之事。尚不能奋决而行之。臣恐 殿下之志犹未有坚确立定者。而所谓省察于行事之间者。犹有所未至也。臣为是悯焉。林泳曰。朴泰辅之言。非主于万铁一事。姑就事之十分明白者。欲赞 殿下既知必行之志尔。十七日。泰辅上疏曰。臣窃意玉堂与两司。同有言议之责。劄褫台谏则有旧章。筵中奏事。乃真筵臣之所。则苟有所见。不当泛论得失而已。故臣之论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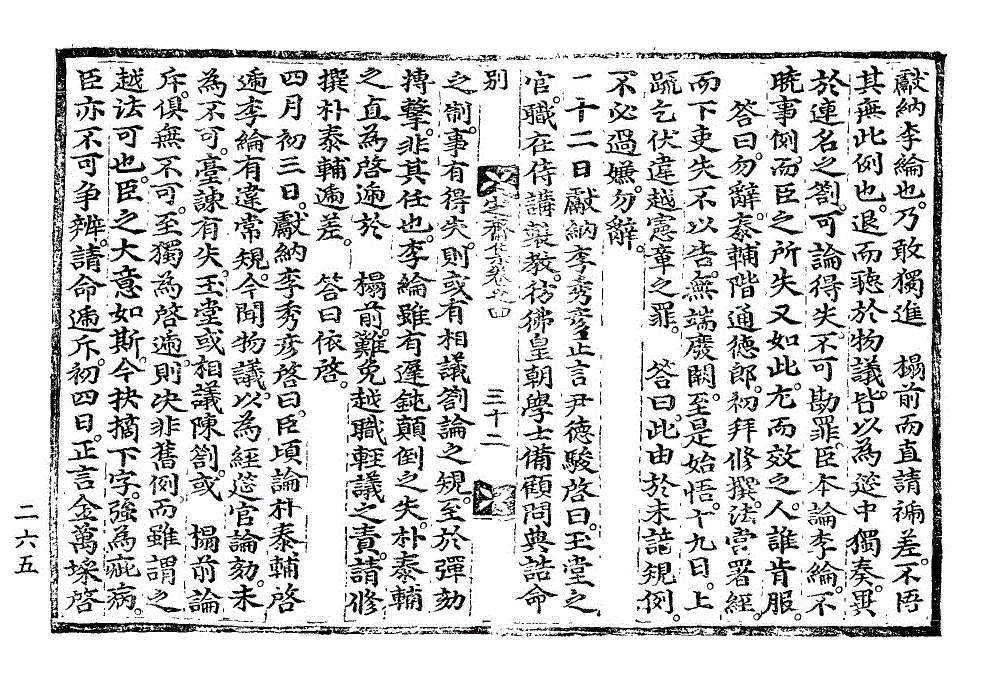 献纳李纶也。乃敢独进 榻前而直请褫差。不悟其无此例也。退而听于物议。皆以为筵中独奏。异于连名之劄。可论得失。不可勘罪。臣本论李纶。不晓事例。而臣之所失又如此。尤而效之。人谁肯服。 答曰。勿辞。泰辅阶通德郎。初拜修撰。法当署经。而下吏失不以告。无端废阙。至是始悟。十九日。上疏乞伏违越宪章之罪。 答曰。此由于未谙规例。不必过嫌。勿辞。
献纳李纶也。乃敢独进 榻前而直请褫差。不悟其无此例也。退而听于物议。皆以为筵中独奏。异于连名之劄。可论得失。不可勘罪。臣本论李纶。不晓事例。而臣之所失又如此。尤而效之。人谁肯服。 答曰。勿辞。泰辅阶通德郎。初拜修撰。法当署经。而下吏失不以告。无端废阙。至是始悟。十九日。上疏乞伏违越宪章之罪。 答曰。此由于未谙规例。不必过嫌。勿辞。二十二日献纳李秀彦,正言尹德骏启曰。玉堂之官。职在侍讲制教。彷佛皇朝学士备顾问典诰命之制。事有得失。则或有相议劄论之规。至于弹劾搏击。非其任也。李纶虽有迟钝颠倒之失。朴泰辅之直为启递于 榻前。难免越职轻议之责。请修撰朴泰辅递差。 答曰依启。
辛酉四月
初三日。献纳李秀彦启曰。臣顷论朴泰辅启递李纶有违常规。今闻物议。以为经筵官论劾。未为不可。台谏有失。玉堂或相议陈劄。或 榻前论斥。俱无不可。至独为启递。则决非旧例。而虽谓之越法可也。臣之大意如斯。今抉摘下字。强为疵病。臣亦不可争辨。请命递斥。初四日。正言金万埰启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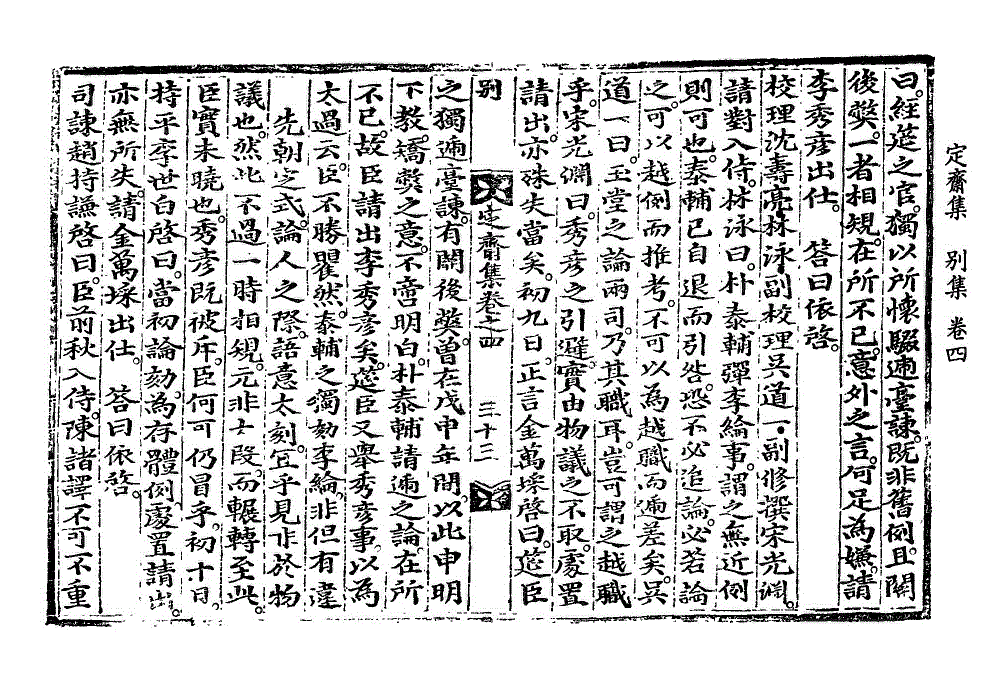 曰。经筵之官。独以所怀䮕递台谏。既非旧例。且关后弊。一者相规。在所不已。意外之言。何足为嫌。请李秀彦出仕。 答曰依启。
曰。经筵之官。独以所怀䮕递台谏。既非旧例。且关后弊。一者相规。在所不已。意外之言。何足为嫌。请李秀彦出仕。 答曰依启。校理沈寿亮,林泳,副校理吴道一,副修撰宋光渊。请对入侍。林泳曰。朴泰辅弹李纶事。谓之无近例则可也。泰辅已自退而引咎。恐不必追论。必若论之。可以越例而推考。不可以为越职而递差矣。吴道一曰。玉堂之论两司。乃其职耳。岂可谓之越职乎。宋光渊曰。秀彦之引避。实由物议之不取。处置请出。亦殊失当矣。初九日。正言金万埰启曰。筵臣之独递台谏。有关后弊。曾在戊申年间。以此申明下教。矫弊之意。不啻明白。朴泰辅请递之论。在所不已。故臣请出李秀彦矣。筵臣又举秀彦事。以为太过云。臣不胜瞿然。泰辅之独劾李纶。非但有违 先朝定式。论人之际。语意太刻。宜乎见非于物议也。然此不过一时相规。元非大段。而辗转至此。臣实未晓也。秀彦既被斥。臣何可仍冒乎。初十日。持平李世白启曰。当初论劾。为存体例。处置请出。亦无所失。请金万埰出仕。 答曰依启。
司谏赵持谦启曰。臣前秋入侍。陈诸译不可不重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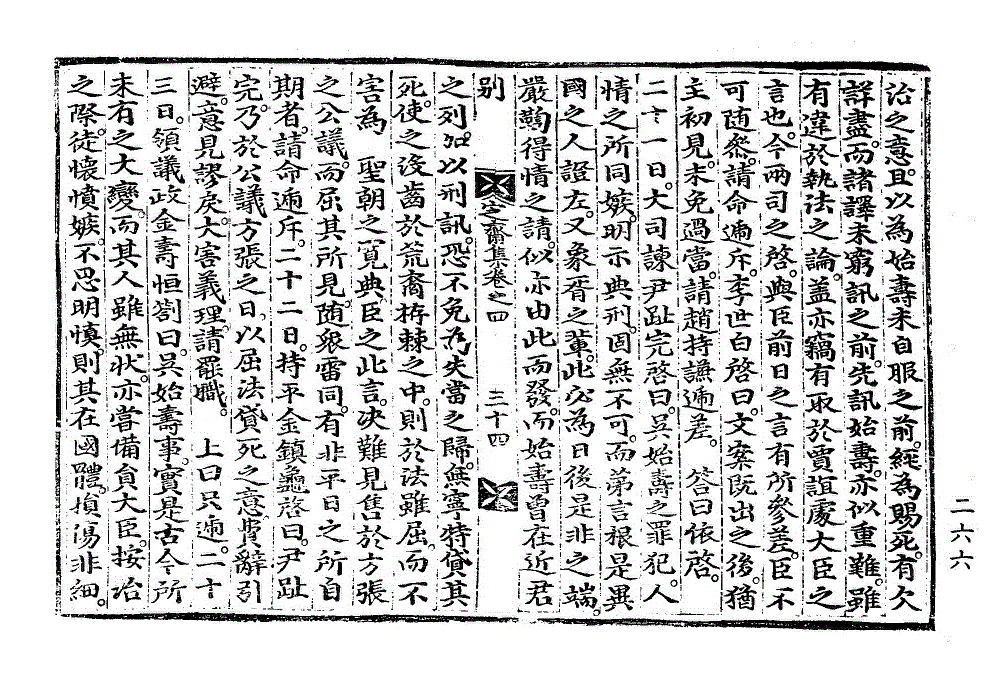 治之意。且以为始寿未自服之前。经为赐死。有欠详尽。而诸译未穷讯之前。先讯始寿。亦似重难。虽有违于执法之论。盖亦窃有取于贾谊处大臣之言也。今两司之启。与臣前日之言有所参差。臣不可随参。请命递斥。李世白启曰。文案既出之后。犹主初见。未免过当。请赵持谦递差。 答曰依启。
治之意。且以为始寿未自服之前。经为赐死。有欠详尽。而诸译未穷讯之前。先讯始寿。亦似重难。虽有违于执法之论。盖亦窃有取于贾谊处大臣之言也。今两司之启。与臣前日之言有所参差。臣不可随参。请命递斥。李世白启曰。文案既出之后。犹主初见。未免过当。请赵持谦递差。 答曰依启。二十一日。大司谏尹趾完启曰。吴始寿之罪犯。人情之所同嫉。明示典刑。固无不可。而第言根是异国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辈。此必为日后是非之端。严鞫得情之请。似亦由此而发。而始寿曾在近君之列。加以刑讯。恐不免为失当之归。无宁特贷其死。使之没齿于荒裔栫棘之中。则于法虽屈。而不害为 圣朝之宽典。臣之此言。决难见售于方张之公议。而屈其所见。随众雷同。有非平日之所自期者。请命递斥。二十二日。持平金镇龟启曰。尹趾完。乃于公议方张之日。以屈法贷死之意。费辞引避。意见谬戾。大害义理。请罢职。 上曰只递。二十三日。领议政金寿恒劄曰。吴始寿事。实是古今所未有之大变。而其人虽无状。亦尝备员大臣。按治之际。徒怀愤嫉。不思明慎。则其在国体。损伤非细。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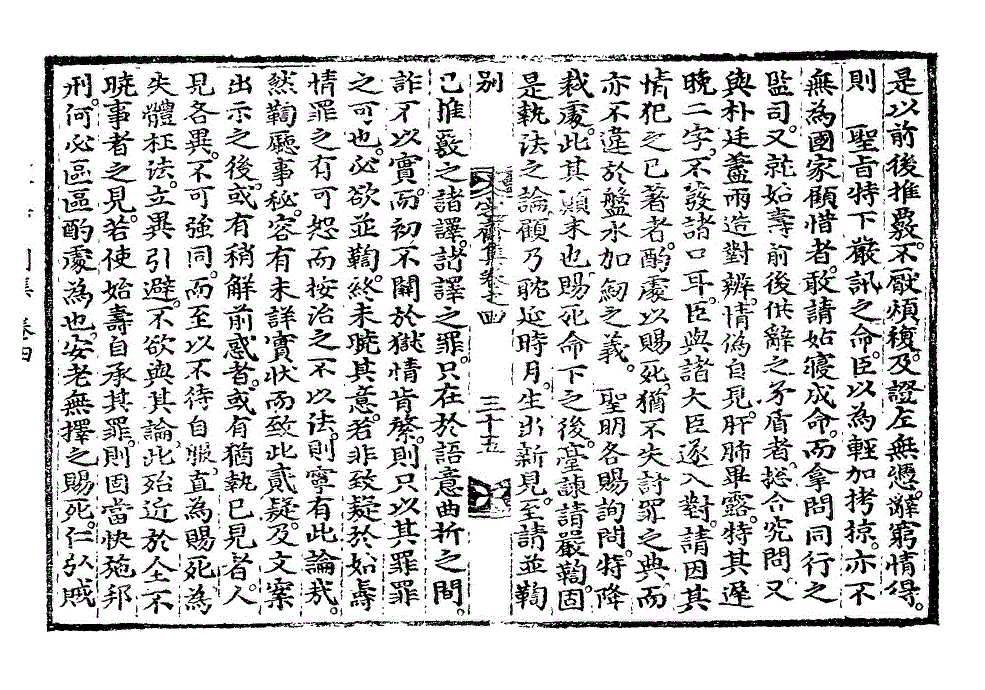 是以前后推覈。不厌烦复。及證左无凭。辞穷情得。则 圣旨特下严讯之命。臣以为轻加拷掠。亦不无为国家顾惜者。敢请姑寝成命。而拿问同行之监司。又就始寿前后供辞之矛盾者。总合究问。又与朴廷荩两造对辨。情伪自见。肝肺毕露。特其迟晚二字。不发诸口耳。臣与诸大臣遂入对。请因其情犯之已著者。酌处以赐死。犹不失讨罪之典。而亦不违于盘水加剑之义。 圣明各赐询问。特降裁处。此其颠末也。赐死命下之后。台谏请严鞫。固是执法之论。顾乃耽延时月。生出新见。至请并鞫已推覈之诸译。诸译之罪。只在于语意曲折之间。诈不以实。而初不关于狱情肯綮。则只以其罪罪之可也。必欲并鞫。终未晓其意。若非致疑于始寿情罪之有可恕而按治之不以法。则宁有此论哉。然鞫厅事秘。容有未详实状而致此贰疑。及文案出示之后。或有稍解前惑者。或有犹执己见者。人见各异。不可强同。而至以不待自服。直为赐死。为失体枉法。立异引避。不欲与其论。此殆近于全不晓事者之见。若使始寿自承其罪。则固当快施邦刑。何必区区酌处为也。安老无择之赐死。仁弘贼
是以前后推覈。不厌烦复。及證左无凭。辞穷情得。则 圣旨特下严讯之命。臣以为轻加拷掠。亦不无为国家顾惜者。敢请姑寝成命。而拿问同行之监司。又就始寿前后供辞之矛盾者。总合究问。又与朴廷荩两造对辨。情伪自见。肝肺毕露。特其迟晚二字。不发诸口耳。臣与诸大臣遂入对。请因其情犯之已著者。酌处以赐死。犹不失讨罪之典。而亦不违于盘水加剑之义。 圣明各赐询问。特降裁处。此其颠末也。赐死命下之后。台谏请严鞫。固是执法之论。顾乃耽延时月。生出新见。至请并鞫已推覈之诸译。诸译之罪。只在于语意曲折之间。诈不以实。而初不关于狱情肯綮。则只以其罪罪之可也。必欲并鞫。终未晓其意。若非致疑于始寿情罪之有可恕而按治之不以法。则宁有此论哉。然鞫厅事秘。容有未详实状而致此贰疑。及文案出示之后。或有稍解前惑者。或有犹执己见者。人见各异。不可强同。而至以不待自服。直为赐死。为失体枉法。立异引避。不欲与其论。此殆近于全不晓事者之见。若使始寿自承其罪。则固当快施邦刑。何必区区酌处为也。安老无择之赐死。仁弘贼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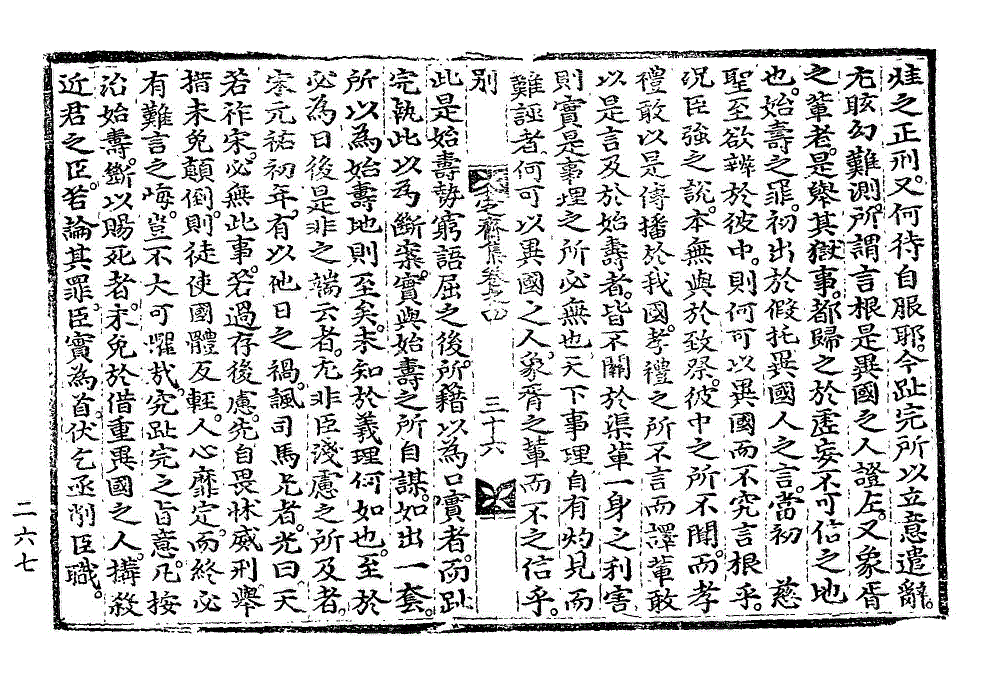 烓之正刑。又何待自服耶。今趾完所以立意遣辞。尤眩幻难测。所谓言根是异国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辈者。是举其狱事。都归之于虚妄不可信之地也。始寿之罪。初出于假托异国人之言。当初 慈圣至欲辨于彼中。则何可以异国而不究言根乎。况臣强之说。本无与于致祭。彼中之所不闻。而孝礼敢以是传播于我国。孝礼之所不言而译辈敢以是言及于始寿者。皆不关于渠辈一身之利害。则实是事理之所必无也。天下事理自有灼见而难诬者。何可以异国之人。象胥之辈而不之信乎。此是始寿势穷语屈之后。所藉以为口实者。而趾完执此以为断案。实与始寿之所自谋。如出一套。所以为始寿地则至矣。未知于义理何如也。至于必为日后是非之端云者。尤非臣浅虑之所及者。宋元祐初年。有以他日之祸。讽司马光者。光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若过存后虑。先自畏怵威刑。举措未免颠倒。则徒使国体反轻。人心靡定。而终必有难言之悔。岂不大可惧哉。究趾完之旨意。凡按治始寿。断以赐死者。未免于借重异国之人。搆杀近君之臣。若论其罪。臣实为首。伏乞亟削臣职。
烓之正刑。又何待自服耶。今趾完所以立意遣辞。尤眩幻难测。所谓言根是异国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辈者。是举其狱事。都归之于虚妄不可信之地也。始寿之罪。初出于假托异国人之言。当初 慈圣至欲辨于彼中。则何可以异国而不究言根乎。况臣强之说。本无与于致祭。彼中之所不闻。而孝礼敢以是传播于我国。孝礼之所不言而译辈敢以是言及于始寿者。皆不关于渠辈一身之利害。则实是事理之所必无也。天下事理自有灼见而难诬者。何可以异国之人。象胥之辈而不之信乎。此是始寿势穷语屈之后。所藉以为口实者。而趾完执此以为断案。实与始寿之所自谋。如出一套。所以为始寿地则至矣。未知于义理何如也。至于必为日后是非之端云者。尤非臣浅虑之所及者。宋元祐初年。有以他日之祸。讽司马光者。光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若过存后虑。先自畏怵威刑。举措未免颠倒。则徒使国体反轻。人心靡定。而终必有难言之悔。岂不大可惧哉。究趾完之旨意。凡按治始寿。断以赐死者。未免于借重异国之人。搆杀近君之臣。若论其罪。臣实为首。伏乞亟削臣职。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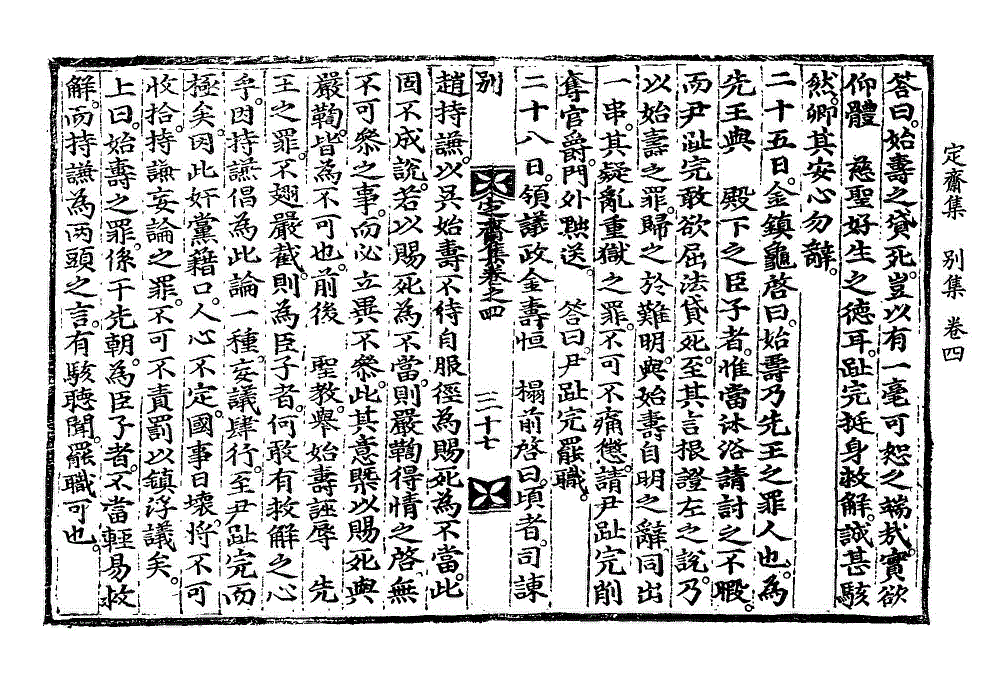 答曰。始寿之贷死。岂以有一毫可恕之端哉。实欲仰体 慈圣好生之德耳。趾完挺身救解。诚甚骇然。卿其安心勿辞。
答曰。始寿之贷死。岂以有一毫可恕之端哉。实欲仰体 慈圣好生之德耳。趾完挺身救解。诚甚骇然。卿其安心勿辞。二十五日。金镇龟启曰。始寿乃先王之罪人也。为先王与 殿下之臣子者。惟当沐浴请讨之不暇。而尹趾完敢欲屈法贷死。至其言根證左之说。乃以始寿之罪。归之于难明。与始寿自明之辞。同出一串。其疑乱重狱之罪。不可不痛惩。请尹趾完削夺官爵。门外黜送。 答曰。尹趾完罢职。
二十八日。领议政金寿恒 榻前启曰。顷者。司谏赵持谦。以吴始寿不待自服径为赐死为不当。此固不成说。若以赐死为不当。则严鞫得情之启。无不可参之事。而必立异不参。此其意槩以赐死与严鞫。皆为不可也。前后 圣教。举始寿诬辱 先王之罪。不翅严截。则为臣子者。何敢有救解之心乎。因持谦倡为此论一种。妄议肆行。至尹趾完而极矣。因此奸党藉口。人心不定。国事日坏。将不可收拾。持谦妄论之罪。不可不责罚以镇浮议矣。 上曰。始寿之罪。系干先朝。为臣子者。不当轻易救解。而持谦为两头之言。有骇听闻。罢职可也。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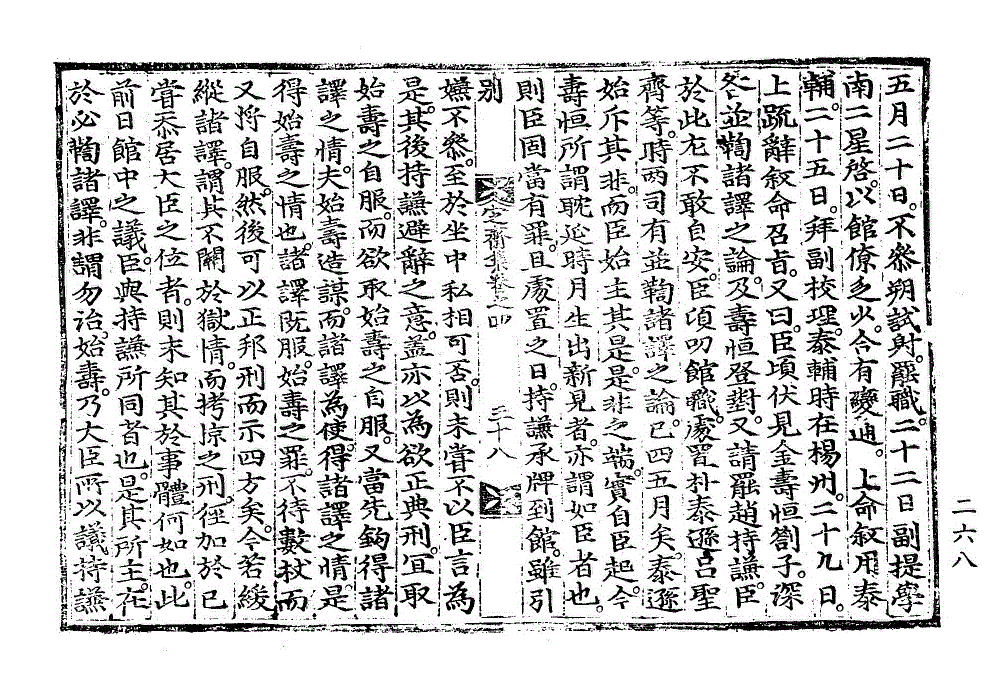 辛酉五月
辛酉五月二十日。不参朔试射。罢职。二十二日副提学南二星启。以馆僚乏少。合有变通。 上命叙用泰辅。二十五日。拜副校理。泰辅时在杨州。二十九日。上疏辞叙命召旨。又曰。臣顷伏见金寿恒劄子。深咎并鞫诸译之论。及寿恒登对。又请罢赵持谦。臣于此尤不敢自安。臣顷叨馆职。处置朴泰逊,吕圣齐等。时两司有并鞫诸译之论。已四五月矣。泰逊始斥其非。而臣始主其是。是非之端。实自臣起。今寿恒所谓耽延时月生出新见者。亦谓如臣者也。则臣固当有罪。且处置之日。持谦承牌到馆。虽引嫌不参。至于坐中私相可否。则未尝不以臣言为是。其后持谦避辞之意。盖亦以为欲正典刑。宜取始寿之自服。而欲取始寿之自服。又当先钩得诸译之情。夫始寿造谋。而诸译为使。得诸译之情。是得始寿之情也。诸译既服。始寿之罪。不待数杖而又将自服。然后可以正邦刑而示四方矣。今若缓纵诸译。谓其不关于狱情。而拷掠之刑。径加于已尝忝居大臣之位者。则未知其于事体何如也。此前日馆中之议。臣与持谦所同者也。是其所主。在于必鞫诸译。非谓勿治。始寿。乃大臣所以议持谦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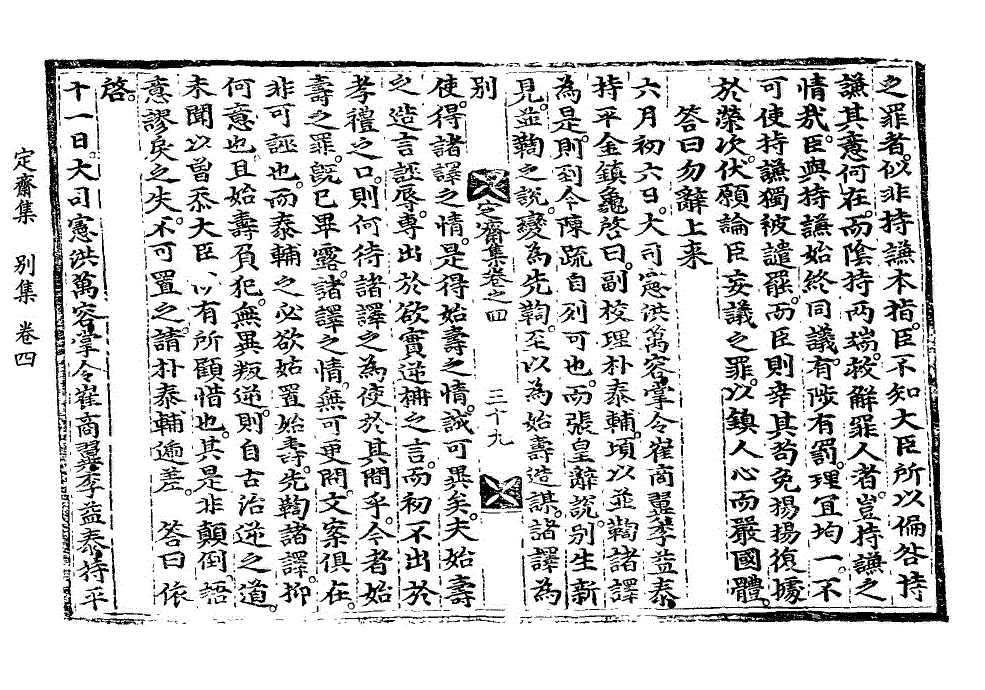 之罪者。似非持谦本指。臣不知大臣所以偏咎持谦其意何在。而阴持两端。救解罪人者。岂持谦之情哉。臣与持谦始终同议。有陟有罚。理宜均一。不可使持谦独被谴罢。而臣则幸其苟免扬扬复据于荣次。伏愿论臣妄议之罪。以镇人心而严国体。 答曰勿辞上来。
之罪者。似非持谦本指。臣不知大臣所以偏咎持谦其意何在。而阴持两端。救解罪人者。岂持谦之情哉。臣与持谦始终同议。有陟有罚。理宜均一。不可使持谦独被谴罢。而臣则幸其苟免扬扬复据于荣次。伏愿论臣妄议之罪。以镇人心而严国体。 答曰勿辞上来。辛酉六月
初六日。大司宪洪万容,掌令崔商翼,李益泰,持平金镇龟启曰。副校理朴泰辅。顷以并鞫诸译为是。则到今陈疏自列可也。而张皇辞说。别生新见。并鞫之说。变为先鞫。至以为始寿造谋。诸译为使。得诸译之情。是得始寿之情。诚可异矣。夫始寿之造言诬辱。专出于欲实逆楠之言。而初不出于孝礼之口。则何待诸译之为使于其间乎。今者始寿之罪。既已毕露。诸译之情。无可更问。文案俱在。非可诬也。而泰辅之必欲姑置始寿。先鞫诸译。抑何意也。且始寿负犯。无异叛逆。则自古治逆之道。未闻以曾忝大臣以有所顾惜也。其是非颠倒。语意谬戾之失。不可置之。请朴泰辅递差。 答曰依启。
十一日。大司宪洪万容,掌令崔商翼,李益泰,持平
定斋别集卷之四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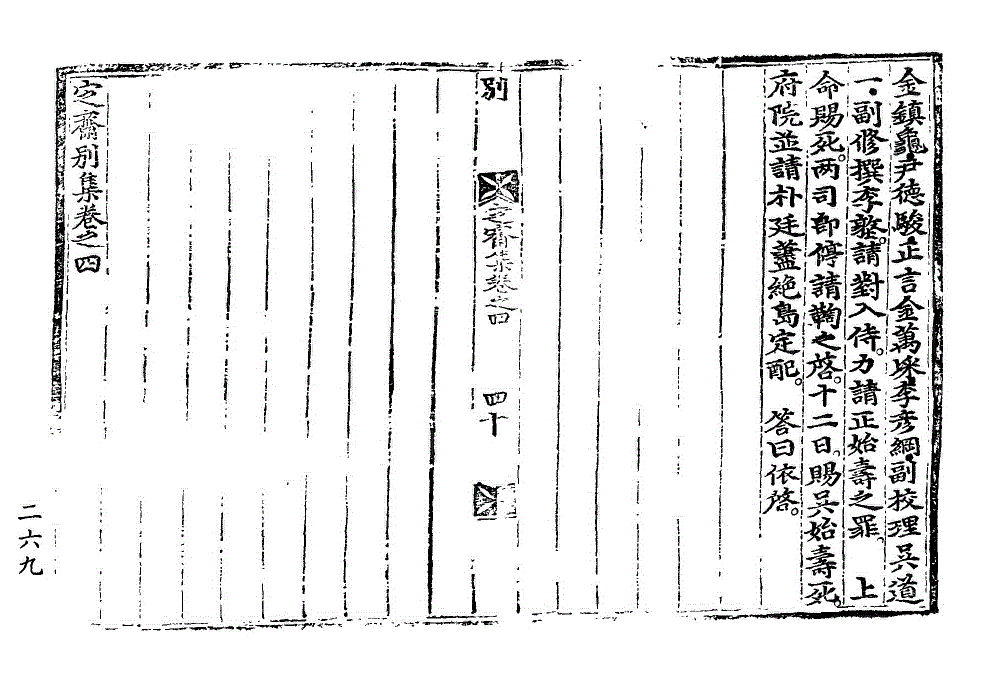 金镇龟,尹德骏,正言金万埰,李彦纲,副校理吴道一,副修撰李墩。请对入侍。力请正始寿之罪。 上命赐死。两司即停请鞫之启。十二日。赐吴始寿死。府院并请朴廷荩绝岛定配。 答曰依启。
金镇龟,尹德骏,正言金万埰,李彦纲,副校理吴道一,副修撰李墩。请对入侍。力请正始寿之罪。 上命赐死。两司即停请鞫之启。十二日。赐吴始寿死。府院并请朴廷荩绝岛定配。 答曰依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