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x 页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杂录]
[杂录]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0H 页
 杂录(壬午)
杂录(壬午)看或问诚意章。略有分晓处。辄为差排如左。
自欺之根没奈何。只可责知至。所谓欠分数。
自欺之萌。容著在这里。诈伪方现。故可猛治。
自欺之干。小人閒居。其欺诈方肆。
自欺之萌。与自欺之干。虽微著嫩壮不同。终是一体相串来也。欠了分数。其等位忒高。
阅读书录要语。有味乎无欲则所行自简等说话。凡人于人伦合做底事。用意当十分坚实。至于奉身调度事系外面者。或得或失。只以悠悠聊且之意遣之为可。
思所当然与所以然之妙而未能融彻。忽见鹰在架上。乃思鹰之捉雉而食。是乃当然。而其所以必捉雉而食者。则以其禀得肃杀之气。故不能甘柔淡之物。若究其禀得杀气之故。则五行中偏得金气故也。是乃理之筑著处。格之造极处。复欲上究其去处。则只曰自然而已。或问中所云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即所当然之故。盖就一理。截为本末。论语注所云事物所以当然之故。正谓是也。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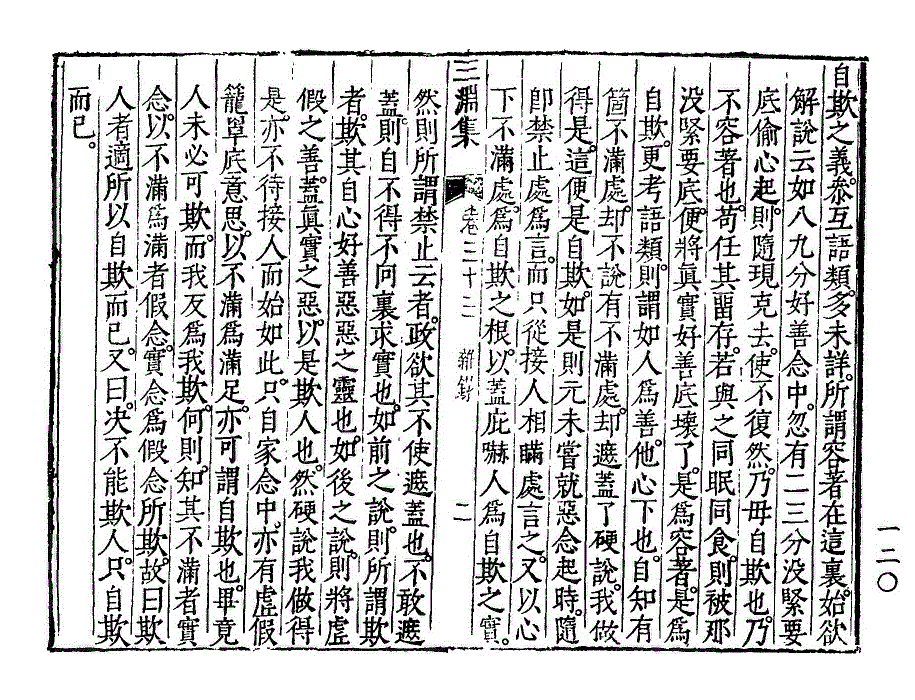 自欺之义。参互语类。多未详。所谓容著在这里。始欲解说云如八九分好善念中。忽有二三分没紧要底偷心起。则随现克去。使不复然。乃毋自欺也。乃不容著也。苟任其留存。若与之同眠同食。则被那没紧要底。便将真实好善底坏了。是为容著。是为自欺。更考语类。则谓如人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个不满处。却不说有不满处。却遮盖了硬说。我做得是。这便是自欺。如是则元未尝就恶念起时。随即禁止处为言。而只从接人相瞒处言之。又以心下不满处。为自欺之根。以盖庇吓人为自欺之实。然则所谓禁止云者。政欲其不使遮盖也。不敢遮盖。则自不得不向里求实也。如前之说。则所谓欺者。欺其自心好善恶恶之灵也。如后之说。则将虚假之善。盖真实之恶。以是欺人也。然硬说我做得是。亦不待接人而始如此。只自家念中。亦有虚假笼罩底意思。以不满为满足。亦可谓自欺也。毕竟人未必可欺。而我反为我欺。何则。知其不满者实念。以不满为满者假念。实念为假念所欺。故曰欺人者适所以自欺而已。又曰。决不能欺人。只自欺而已。
自欺之义。参互语类。多未详。所谓容著在这里。始欲解说云如八九分好善念中。忽有二三分没紧要底偷心起。则随现克去。使不复然。乃毋自欺也。乃不容著也。苟任其留存。若与之同眠同食。则被那没紧要底。便将真实好善底坏了。是为容著。是为自欺。更考语类。则谓如人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个不满处。却不说有不满处。却遮盖了硬说。我做得是。这便是自欺。如是则元未尝就恶念起时。随即禁止处为言。而只从接人相瞒处言之。又以心下不满处。为自欺之根。以盖庇吓人为自欺之实。然则所谓禁止云者。政欲其不使遮盖也。不敢遮盖。则自不得不向里求实也。如前之说。则所谓欺者。欺其自心好善恶恶之灵也。如后之说。则将虚假之善。盖真实之恶。以是欺人也。然硬说我做得是。亦不待接人而始如此。只自家念中。亦有虚假笼罩底意思。以不满为满足。亦可谓自欺也。毕竟人未必可欺。而我反为我欺。何则。知其不满者实念。以不满为满者假念。实念为假念所欺。故曰欺人者适所以自欺而已。又曰。决不能欺人。只自欺而已。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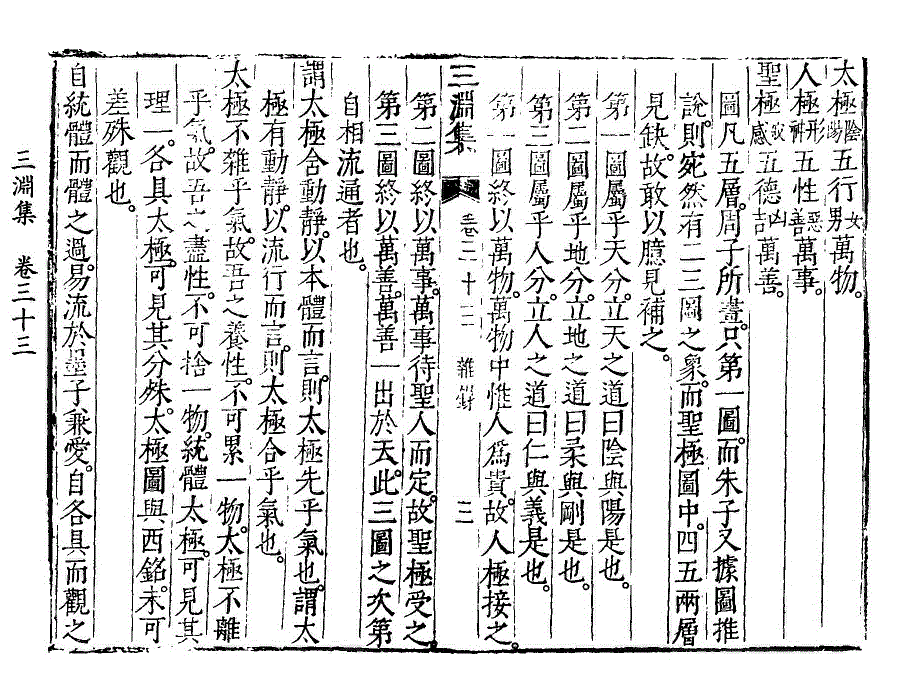 太极(阴阳)五行(女男)万物。
太极(阴阳)五行(女男)万物。人极(形神)五性(恶善)万事。
圣极(寂感)五德(凶吉)万善。
图凡五层。周子所画。只第一图。而朱子又据图推说。则宛然有二三图之象。而圣极图中。四五两层见缺。故敢以臆见补之。
第一图属乎天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是也。
第二图属乎地分。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是也。
第三图属乎人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也。
第一图终以万物。万物中惟人为贵。故人极接之。
第二图终以万事。万事待圣人而定。故圣极受之。
第三图终以万善。万善一出于天。此三图之次第自相流通者也。
谓太极含动静。以本体而言。则太极先乎气也。谓太极有动静。以流行而言。则太极合乎气也。
太极不杂乎气。故吾之养性。不可累一物。太极不离乎气。故吾之尽性。不可舍一物。统体太极。可见其理一。各具太极。可见其分殊。太极图与西铭。未可差殊观也。
自统体而体之过。易流于墨子兼爱。自各具而观之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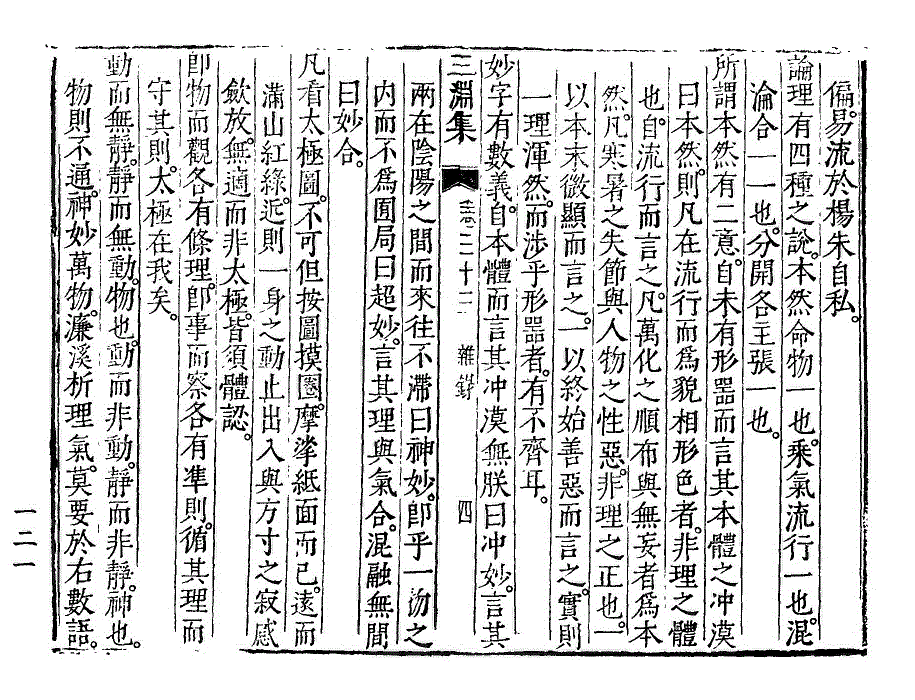 偏。易流于杨朱自私。
偏。易流于杨朱自私。论理有四种之说。本然命物一也。乘气流行一也。混沦合一一也。分开各主张一也。
所谓本然有二意。自未有形器而言其本体之冲漠曰本然。则凡在流行而为貌相形色者。非理之体也。自流行而言之。凡万化之顺布与无妄者为本然。凡寒暑之失节与人物之性恶。非理之正也。一以本末微显而言之。一以终始善恶而言之。实则一理浑然。而涉乎形器者。有不齐耳。
妙字有数义。自本体而言其冲漠无朕曰冲妙。言其两在阴阳之间而来往不滞曰神妙。即乎一物之内而不为囿局曰超妙。言其理与气合。混融无间曰妙合。
凡看太极图。不可但按图摸圈。摩挲纸面而已。远而满山红绿。近则一身之动止出入与方寸之寂感敛放。无适而非太极。皆须体认。
即物而观各有条理。即事而察各有准则。循其理而守其则。太极在我矣。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非动。静而非静。神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濂溪析理气。莫要于右数语。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日录(己亥)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2H 页
 三月
三月初一日
微雨风恬。杜鹃花始开。斗奴出山去。借得睡庵僧供炊。庭院阒寂。惟有鸟声。
看二程全书。其论人物同具五常。甚分晓。聊记于左。
天有五气。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黄者得土之性多。白者得金之性多。
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物则不推。人则能推。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
只此三条。足可破近世儱侗之说。知有此说而犹且执拗。则便是互乡。
尝以五棱木面。刻金木水火土。轮而看之。居一而有其四。宛然可见。或曰。大黄只大黄。附子只附子。而余则曰。大黄之内伏附子。附子之内伏大黄。如水火之内外明暗。迭为换面耳。
春秋之学。程子看作大事。朱子甚忽之。以孟子知我罪我之言折之。终有未可忽者。盖四传多穿凿。故朱子未免激恼。至谓鲁史旧文。圣人笔削。干我甚事。则恐亦太过矣。当初作经时。鲁史与之并行。则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2L 页
 人见笔削而参校之。可会其微意。今则鲁史亡矣。无凭可考。所以为难解也。名字书不书。以是为褒贬。亦难尽扫去。朱子论春秋。只以据事直书为主。亦少意味。恐须参程子讲解而究之以夏时冠周月。程子之说。亦不可从周。只是改月不改时耳。王阳明论此颇爽利。
人见笔削而参校之。可会其微意。今则鲁史亡矣。无凭可考。所以为难解也。名字书不书。以是为褒贬。亦难尽扫去。朱子论春秋。只以据事直书为主。亦少意味。恐须参程子讲解而究之以夏时冠周月。程子之说。亦不可从周。只是改月不改时耳。王阳明论此颇爽利。春秋公孙敖始末。郑重书之。恶其奔莒而美鲁之不薄耶。
赵盾弑其君。以功意言之。盾为意而穿为功。如欧公说。虽似直截。而终少意味。如郑归生弑君之类。亦诛助恶之意。足为万世法。此等处。岂可以左氏所录。全归之虚妄乎。(如高贵乡公。当书曰司马昭弑其君。不当举成济贾充矣。)
郑伯克段,郑弃其师,鲁成宋乱,纳郜鼎,翚帅师之类。辞气严厉。最可见。
承讹袭谬。在大贤所不免。如诗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其破碎乐淫哀伤而凑合为说。可一笔勾断。而以两程之明。不能看破。则滞于闻见也。至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尤为怪事。不有朱子则孰辨真赝乎。至夷齐谏伐事。则七圣皆迷。总输于荆公一只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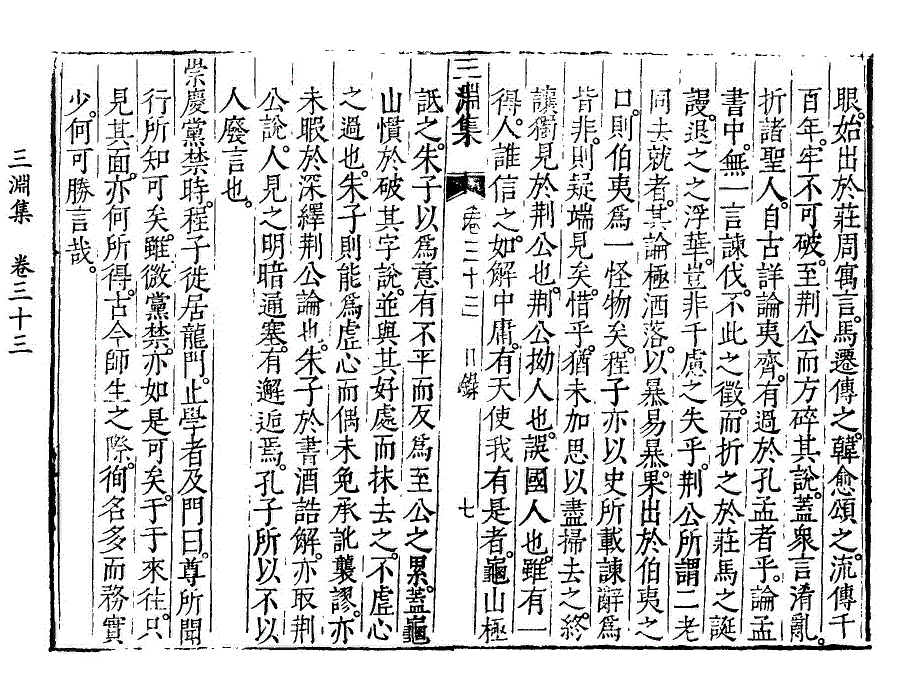 眼。始出于庄周寓言。马迁传之。韩愈颂之。流传千百年。牢不可破。至荆公而方碎其说。盖众言淆乱。折诸圣人。自古详论夷齐。有过于孔孟者乎。论孟书中。无一言谏伐。不此之徵。而折之于庄马之诞谩。退之之浮华。岂非千虑之失乎。荆公所谓二老同去就者。其论极洒落。以暴易暴。果出于伯夷之口。则伯夷为一怪物矣。程子亦以史所载谏辞为皆非。则疑端见矣。惜乎。犹未加思以尽扫去之。终让独见于荆公也。荆公拗人也。误国人也。虽有一得。人谁信之。如解中庸。有天使我有是者。龟山极诋之。朱子以为意有不平而反为至公之累。盖龟山惯于破其字说。并与其好处而抹去之。不虚心之过也。朱子则能为虚心而偶未免承讹袭谬。亦未暇于深绎荆公论也。朱子于书酒诰解。亦取荆公说。人见之明暗通塞。有邂逅焉。孔子所以不以人废言也。
眼。始出于庄周寓言。马迁传之。韩愈颂之。流传千百年。牢不可破。至荆公而方碎其说。盖众言淆乱。折诸圣人。自古详论夷齐。有过于孔孟者乎。论孟书中。无一言谏伐。不此之徵。而折之于庄马之诞谩。退之之浮华。岂非千虑之失乎。荆公所谓二老同去就者。其论极洒落。以暴易暴。果出于伯夷之口。则伯夷为一怪物矣。程子亦以史所载谏辞为皆非。则疑端见矣。惜乎。犹未加思以尽扫去之。终让独见于荆公也。荆公拗人也。误国人也。虽有一得。人谁信之。如解中庸。有天使我有是者。龟山极诋之。朱子以为意有不平而反为至公之累。盖龟山惯于破其字说。并与其好处而抹去之。不虚心之过也。朱子则能为虚心而偶未免承讹袭谬。亦未暇于深绎荆公论也。朱子于书酒诰解。亦取荆公说。人见之明暗通塞。有邂逅焉。孔子所以不以人废言也。崇庆党禁时。程子徙居龙门。止学者及门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虽微党禁。亦如是可矣。于于来往。只见其面。亦何所得。古今师生之际。徇名多而务实少。何可胜言哉。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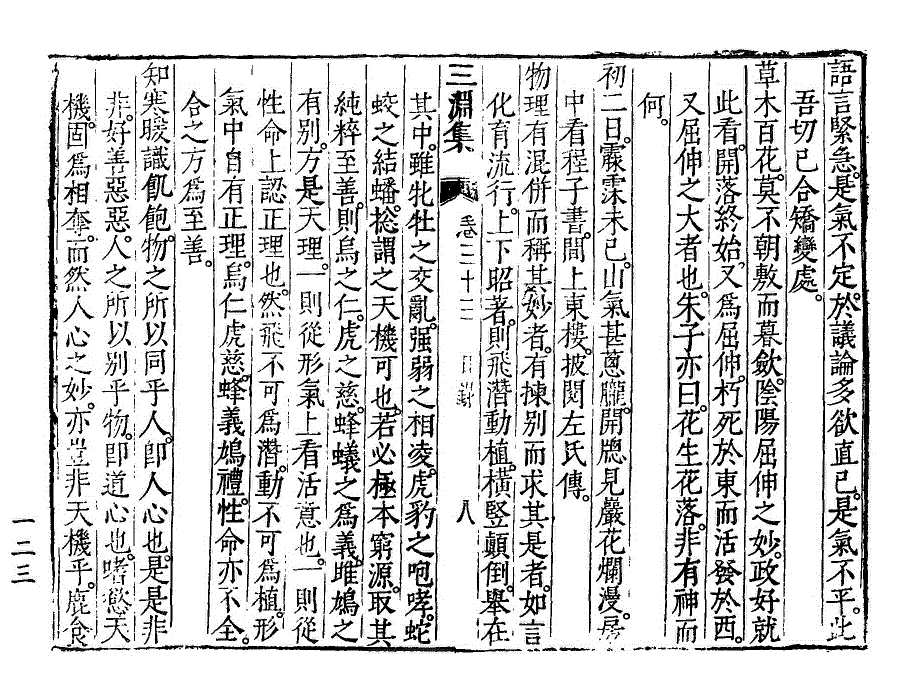 语言紧急。是气不定。于议论多欲直己。是气不平。此吾切己合矫变处。
语言紧急。是气不定。于议论多欲直己。是气不平。此吾切己合矫变处。草木百花。莫不朝敷而暮敛。阴阳屈伸之妙。政好就此看。开落终始。又为屈伸。朽死于东而活发于西。又屈伸之大者也。朱子亦曰。花生花落。非有神而何。
初二日
霢霂未已。山气甚葱胧。开窗见岩花烂漫。房中看程子书。间上东楼。披阅左氏传。
物理有混并而称其妙者。有拣别而求其是者。如言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则飞潜动植。横竖颠倒。举在其中。虽牝牡之交乱。强弱之相凌。虎豹之咆哮。蛇蛟之结蟠。总谓之天机可也。若必极本穷源。取其纯粹至善。则乌之仁。虎之慈。蜂蚁之为义。雎鸠之有别。方是天理。一则从形气上看活意也。一则从性命上认正理也。然飞不可为潜。动不可为植。形气中自有正理。乌仁虎慈。蜂义鸠礼。性命亦不全。合之方为至善。
知寒暖识饥饱。物之所以同乎人。即人心也。是是非非。好善恶恶。人之所以别乎物。即道心也。嗜欲天机。固为相夺。而然人心之妙。亦岂非天机乎。鹿食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4H 页
 雉啄。与耕凿含哺。同一乐意。暝鸟知还。冬虫能蛰。亦岂与向晦宴息。妇子入处异趣乎。至其利义对立。取舍斯判而后。人心逗乃为人欲。方背乎本然天理。今不原来历。不分曲直。而以为气所掩。不能直遂者。谓之人心。人心岂皆不直遂乎。有人于此。痰塞心窍。饥不觅食。渴不求饮。或冬嚼冰而夏就汤。则谓之不直遂可也。
雉啄。与耕凿含哺。同一乐意。暝鸟知还。冬虫能蛰。亦岂与向晦宴息。妇子入处异趣乎。至其利义对立。取舍斯判而后。人心逗乃为人欲。方背乎本然天理。今不原来历。不分曲直。而以为气所掩。不能直遂者。谓之人心。人心岂皆不直遂乎。有人于此。痰塞心窍。饥不觅食。渴不求饮。或冬嚼冰而夏就汤。则谓之不直遂可也。中庸所谓身不失天下之令名。非不满之辞。盖以臣伐君。势似不顺。而实合于天理。不害为万世圣人。故宛转其辞。似若分疏者尔。
朱子于禹贡彭蠡条。不得其解。遂为通变之说。乃谓禹未亲履其地。遣其官属。则官属亦畏三苗而不得深入。只依俙远望。以彭蠡为江汉。东汇以成泽。而实则不然。夫然。禹之作事。大段疏率。何足为神禹乎。此等处。只合阙疑。恐不当别为通变之说以伤体面。无已则巢湖在江北。稍与文义相叶。以是为古之彭蠡可矣。
日月升降三万里。谓夏至冬至。相去三万里。伊川认作东西相去之数。伊川又谓天地无适而非中。朱子以为非是土圭尺五寸。一寸准千里。自冬至极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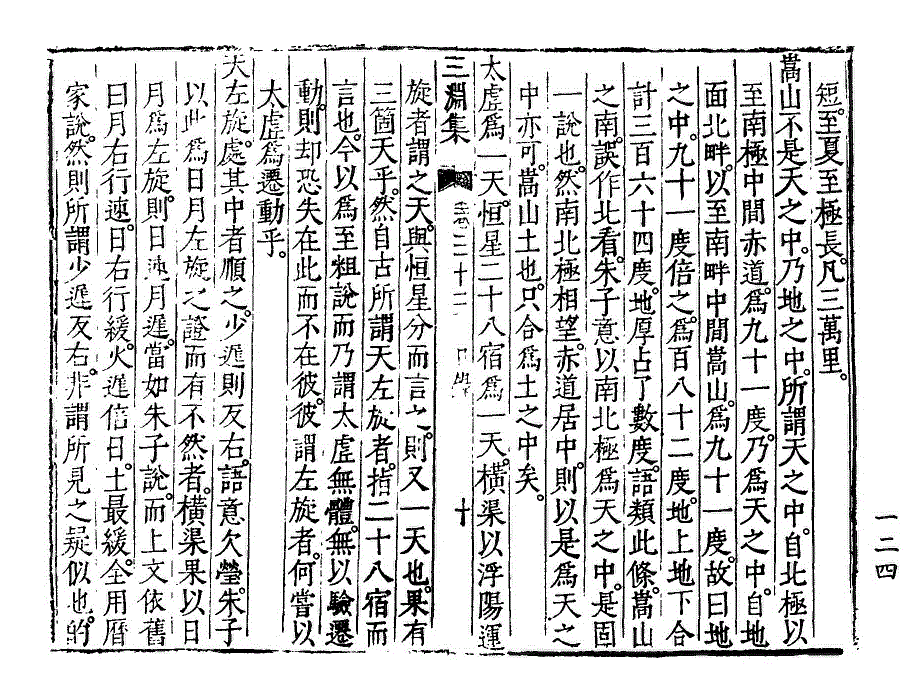 短。至夏至极长。凡三万里。
短。至夏至极长。凡三万里。嵩山不是天之中。乃地之中。所谓天之中。自北极以至南极中间赤道。为九十一度。乃为天之中。自地面北畔。以至南畔中间嵩山。为九十一度。故曰地之中。九十一度倍之。为百八十二度。地上地下合计三百六十四度。地厚占了数度。语类此条。嵩山之南。误作北看。朱子意以南北极为天之中。是固一说也。然南北极相望。赤道居中。则以是为天之中亦可。嵩山土也。只合为土之中矣。
太虚为一天。恒星二十八宿为一天。横渠以浮阳运旋者谓之天。与恒星分而言之。则又一天也。果有三个天乎。然自古所谓天左旋者。指二十八宿而言也。今以为至粗说而乃谓太虚无体。无以验迁动。则却恐失在此而不在彼。彼谓左旋者。何尝以太虚为迁动乎。
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语意欠莹。朱子以此为日月左旋之證而有不然者。横渠果以日月为左旋。则日速月迟。当如朱子说。而上文依旧曰月右行速。日右行缓。火迟倍日。土最缓。全用历家说。然则所谓少迟反右。非谓所见之疑似也。的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5H 页
 言其反右之势耳。语虽未莹。意则可见。朱子于此。似未究其本末曲折。而只取孤句之合意者。持为左旋一證。可疑。
言其反右之势耳。语虽未莹。意则可见。朱子于此。似未究其本末曲折。而只取孤句之合意者。持为左旋一證。可疑。邵子曰。天为父日为子。故天左旋日右旋。这般所在。邵子必看透矣。
杜预曰。日行迟。一岁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李仲谦以为错见。实则仲谦见未到耳。周天有两说。以太虚天而言之。则日之自东而西。西而又东。固一日一周也。如以踏著恒星步数而言之。则日踏一度。至一年而恰周。杜预之说。盖指右旋而言也。
日月左右旋。万古一大讼。明太祖主右旋。而以马上管窥。分明见日月右旋为證。则疏阔莫甚。安城刘氏亦有一说类此。
以阳迟阴速言之。日不及月。于理似乖。白虎通以君逸臣劳为解。亦粗通。
自地面北畔。至极星三十六度。自极星向南圆曲。亦三十六度。合计七十二度。傍亦如之。虽低昂环转。而要在地上而未尝入地矣。
曾子问许多变礼。处之有权。则礼亦易也。易大传。观其会通。以行典礼。则易亦礼也。融而会之。便是一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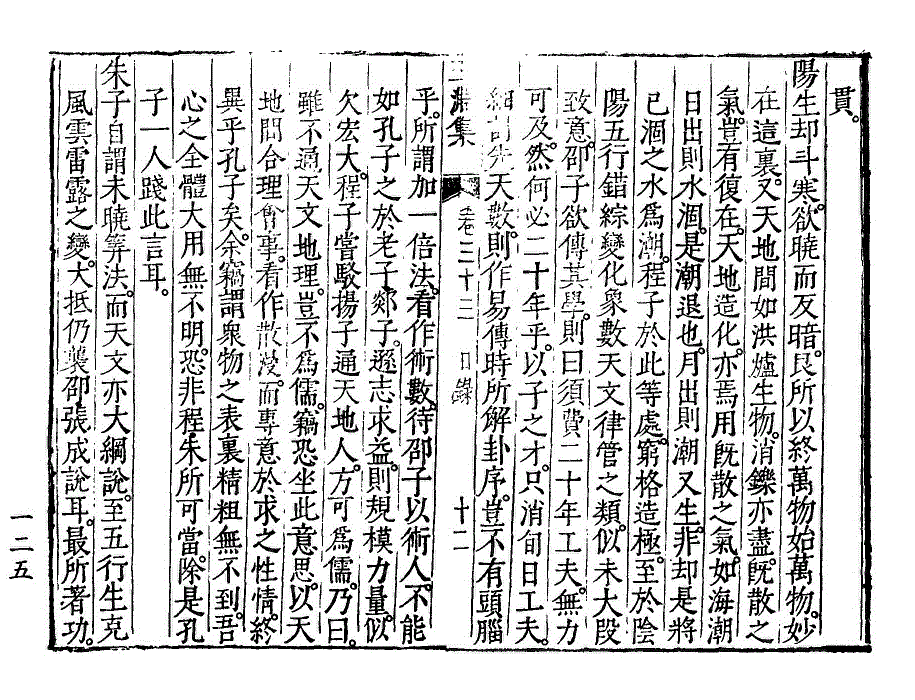 贯。
贯。阳生却斗寒。欲晓而反暗。艮所以终万物始万物。妙在这里。又天地间如洪炉生物。消铄亦尽。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亦焉用既散之气。如海潮日出则水涸。是潮退也。月出则潮又生。非却是将已涸之水为潮。程子于此等处。穷格造极。至于阴阳五行错综变化象数天文律管之类。似未大段致意。邵子欲传其学。则曰须费二十年工夫。无力可及。然何必二十年乎。以子之才。只消旬日工夫。细计先天数。则作易传时所解卦序。岂不有头脑乎。所谓加一倍法。看作术数。待邵子以术人。不能如孔子之于老子,郯子。逊志求益。则规模力量。似欠宏大。程子尝驳扬子通天地人。方可为儒。乃曰。虽不通天文地理。岂不为儒。窃恐坐此意思。以天地间合理会事。看作散漫。而专意于求之性情。终异乎孔子矣。余窃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恐非程,朱所可当。除是孔子一人践此言耳。
朱子自谓未晓算法。而天文亦大纲说。至五行生克风云雷露之变。大抵仍袭邵,张成说耳。最所著功。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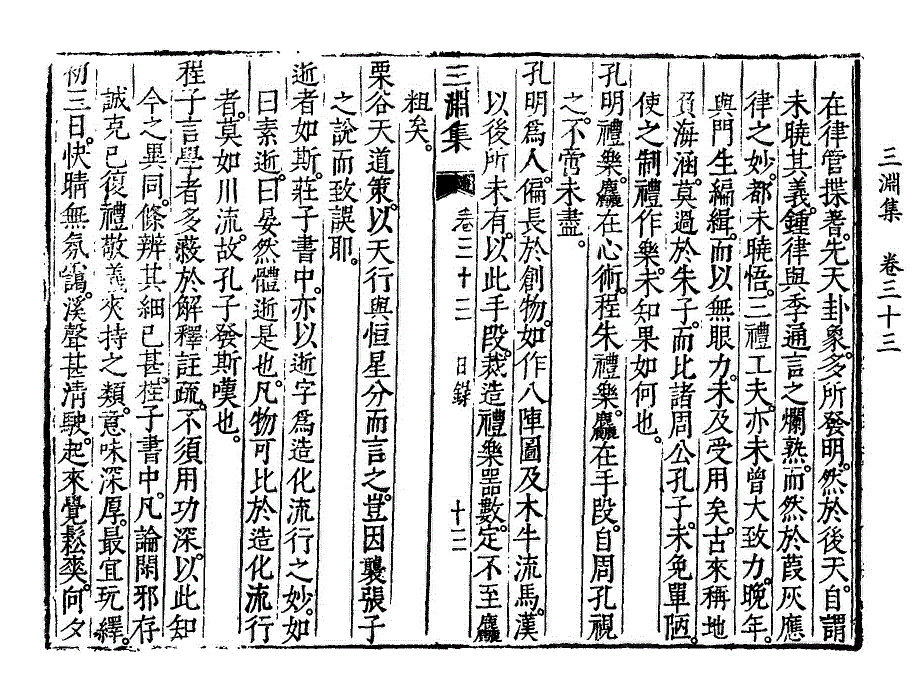 在律管揲蓍。先天卦象。多所发明。然于后天。自谓未晓其义。钟律与季通言之烂熟。而然于葭灰应律之妙。都未晓悟。三礼工夫。亦未曾大致力。晚年。与门生编缉。而以无眼力。未及受用矣。古来称地负海涵。莫过于朱子。而比诸周公孔子。未免单陋。使之制礼作乐。未知果如何也。
在律管揲蓍。先天卦象。多所发明。然于后天。自谓未晓其义。钟律与季通言之烂熟。而然于葭灰应律之妙。都未晓悟。三礼工夫。亦未曾大致力。晚年。与门生编缉。而以无眼力。未及受用矣。古来称地负海涵。莫过于朱子。而比诸周公孔子。未免单陋。使之制礼作乐。未知果如何也。孔明礼乐。粗在心术。程朱礼乐。粗在手段。自周孔视之。不啻未尽。
孔明为人。偏长于创物。如作八阵图及木牛流马。汉以后所未有。以此手段。裁造礼乐器数。定不至粗粗矣。
栗谷天道策。以天行与恒星分而言之。岂因袭张子之说而致误耶。
逝者如斯。庄子书中。亦以逝字为造化流行之妙。如曰素逝。曰晏然体逝是也。凡物可比于造化流行者。莫如川流。故孔子发斯叹也。
程子言学者多蔽于解释注疏。不须用功深。以此知今之异同。条辨其细已甚。程子书中。凡论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敬义夹持之类。意味深厚。最宜玩绎。
初三日
快晴无氛霭。溪声甚清驶。起来觉松爽。向夕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6L 页
 风作。
风作。春秋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注皆误。两君相对。则彼之左。此之右也。左坚而右瑕。故季梁劝随君必攻其右耳。必者须也。左传例多此文法。如从诸注。则连排三句。只言楚君之在左。文无筋骨矣。
郑公子忽再辞齐婚。义正而辞当。至祭仲劝以树援而不从。则尤为坚确。君子之所宜褒美。而解春秋者。以成败为是非。乃谓郑人贱之。又谓孔子称世子而不称君。乃深刺之也。作诗序者。以许多淫奔之诗。皆断为刺忽。吕东莱仍袭其说。锻鍊得郑忽罪不容诛。朱子曰。最是忽可怜。盖诗与春秋相牵连。春秋既错解。则说诗者从而鹘突矣。又可曰因诗序而错解春秋矣。
程子从诗序狡童狂童之说。断之以不能保其位。故不称爵。
孔子之不称伯而称世子。其义亦难明。岂当初未定君位耶。
朱子曰。郑忽岂得做狡童。若是狡童。则必能托婚大国。得其助矣。读至此。不觉发笑。
一年一度花。春节最烂漫。夏秋虽有花。不能如此之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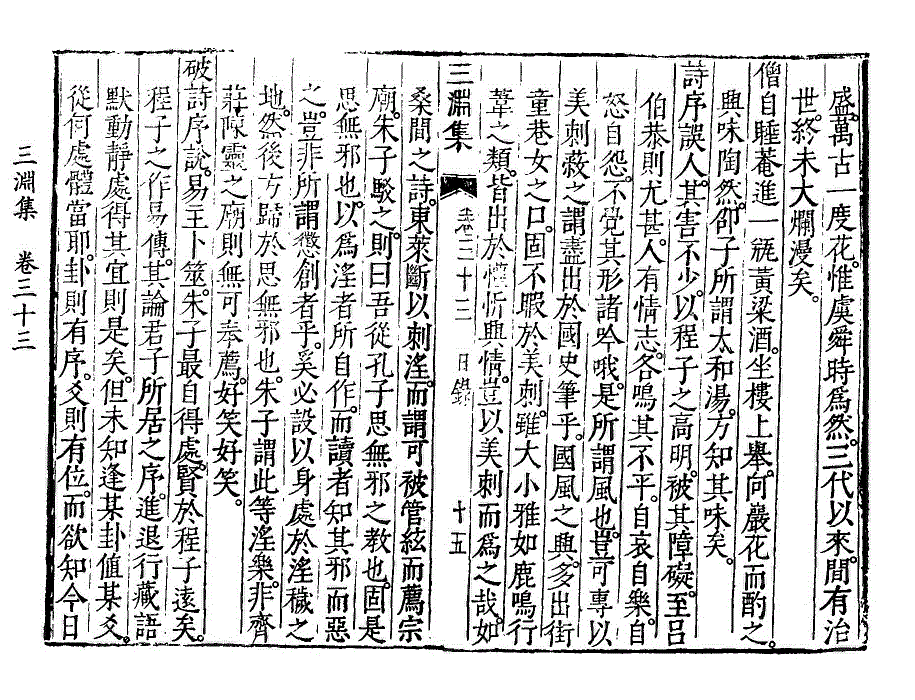 盛。万古一度花。惟虞舜时为然。三代以来。间有治世。终未大烂漫矣。
盛。万古一度花。惟虞舜时为然。三代以来。间有治世。终未大烂漫矣。僧自睡庵进一瓶黄粱酒。坐楼上举。向岩花而酌之。兴味陶然。邵子所谓太和汤。方知其味矣。
诗序误人。其害不少。以程子之高明。被其障碍。至吕伯恭则尤甚。人有情志。各鸣其不平。自哀自乐。自怒自怨。不觉其形诸吟哦。是所谓风也。岂可专以美刺蔽之谓尽出于国史笔乎。国风之兴。多出街童巷女之口。固不暇于美刺。虽大小雅如鹿鸣行苇之类。皆出于欢忻兴情。岂以美刺而为之哉。如桑间之诗。东莱断以刺淫。而谓可被管弦而荐宗庙。朱子驳之。则曰吾从孔子思无邪之教也。固是思无邪也。以为淫者所自作。而读者知其邪而恶之。岂非所谓惩创者乎。奚必设以身处于淫秽之地。然后方归于思无邪也。朱子谓此等淫乐。非齐庄,陈灵之庙则无可奉荐。好笑好笑。
破诗序说。易主卜筮。朱子最自得处。贤于程子远矣。程子之作易传。其论君子所居之序。进退行藏语默动静处得其宜则是矣。但未知逢某卦值某爻。从何处体当耶。卦则有序。爻则有位。而欲知今日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7L 页
 何卦明日何爻。则实无可摸著。若以卜筮推之。则观占玩辞。即可受用。如蒙卦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困卦困于酒食朱韨方来利用享祀之类。说之虽散漫。用之有著落。包蒙则利师资。纳妇则利婚姻。克家则利老传。在酒食为厌饫。在朱韨为缠缚。在祭祀为凑萃。如悬镜于此。妍媸随应。十方无阂。千世不差。所以为玲珑也。程子于此等处。扭捏为一串义理。填塞以许多剩语。如以发蒙立说。则纳妇克家。并为虚说。如取朱韨。则借祭祀以喻诚意而已。朱子所谓伊川多不言实事者是也。盖如朱子说。则象虚而应实。如程子说。则义实而用虚。其得失较然矣。经解洁静精微。易之教也。程子不取其说。以为狭窄。殊不知只此四字。足蔽学易之法。大传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岂非洁静。密岂非精微乎。窃敢谓易传之欠透。恐坐不取经解尔。
何卦明日何爻。则实无可摸著。若以卜筮推之。则观占玩辞。即可受用。如蒙卦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困卦困于酒食朱韨方来利用享祀之类。说之虽散漫。用之有著落。包蒙则利师资。纳妇则利婚姻。克家则利老传。在酒食为厌饫。在朱韨为缠缚。在祭祀为凑萃。如悬镜于此。妍媸随应。十方无阂。千世不差。所以为玲珑也。程子于此等处。扭捏为一串义理。填塞以许多剩语。如以发蒙立说。则纳妇克家。并为虚说。如取朱韨。则借祭祀以喻诚意而已。朱子所谓伊川多不言实事者是也。盖如朱子说。则象虚而应实。如程子说。则义实而用虚。其得失较然矣。经解洁静精微。易之教也。程子不取其说。以为狭窄。殊不知只此四字。足蔽学易之法。大传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岂非洁静。密岂非精微乎。窃敢谓易传之欠透。恐坐不取经解尔。程子曰。文义虽错解。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程子解论语中。错认圣人本旨者。固多有之。义理则纯然无疵。如谢,杨辈则语多外驰。往往沦于佛老。不但错解而已。然理可通行。而听言或未尽。则问东答西。岂不为应物之累乎。明道之动弹流转。似尤于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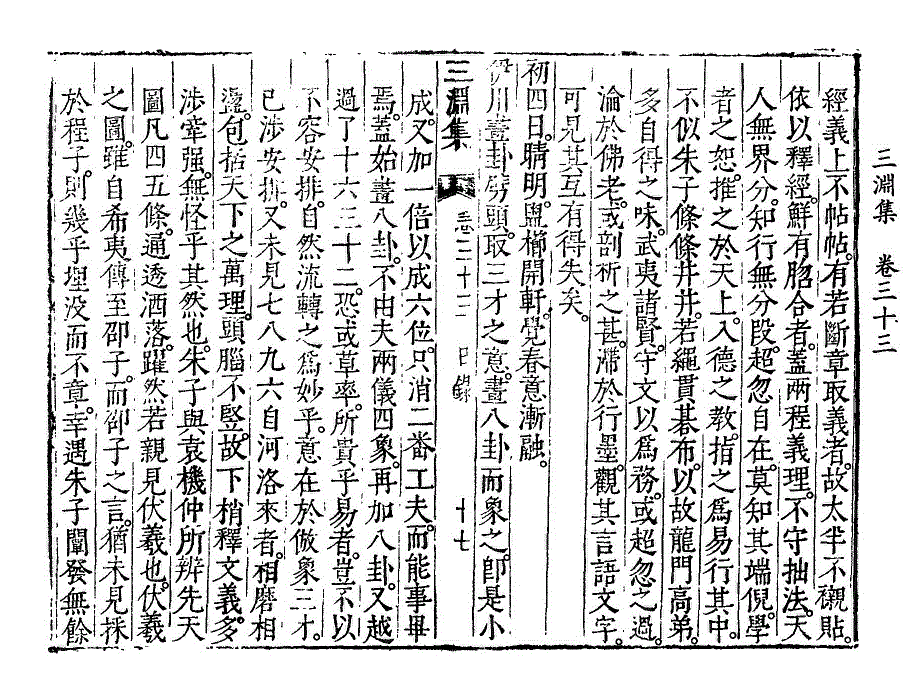 经义上不帖帖。有若断章取义者。故太半不衬贴。依以释经。鲜有吻合者。盖两程义理。不守拙法。天人无界分。知行无分段。超忽自在。莫知其端倪。学者之恕。推之于天上。入德之教。指之为易行其中。不似朱子条条井井。若绳贯棋布。以故龙门高弟。多自得之味。武夷诸贤。守文以为务。或超忽之过。沦于佛老。或剖析之甚。滞于行墨。观其言语文字。可见其互有得失矣。
经义上不帖帖。有若断章取义者。故太半不衬贴。依以释经。鲜有吻合者。盖两程义理。不守拙法。天人无界分。知行无分段。超忽自在。莫知其端倪。学者之恕。推之于天上。入德之教。指之为易行其中。不似朱子条条井井。若绳贯棋布。以故龙门高弟。多自得之味。武夷诸贤。守文以为务。或超忽之过。沦于佛老。或剖析之甚。滞于行墨。观其言语文字。可见其互有得失矣。初四日
晴明。盥栉开轩。觉春意渐融。
伊川画卦劈头。取三才之意。画八卦而象之。即是小成。又加一倍以成六位。只消二番工夫。而能事毕焉。盖始画八卦。不由夫两仪四象。再加八卦。又越过了十六三十二。恐或草率。所贵乎易者。岂不以不容安排。自然流转之为妙乎。意在于仿象三才。已涉安排。又未见七八九六自河洛来者。相磨相荡。包括天下之万理。头脑不竖。故下梢释文义。多涉牵强。无怪乎其然也。朱子与袁机仲所辨先天图凡四五条。通透洒落。跃然若亲见伏羲也。伏羲之图。虽自希夷传至邵子。而邵子之言。犹未见采于程子。则几乎埋没而不章。幸遇朱子阐发无馀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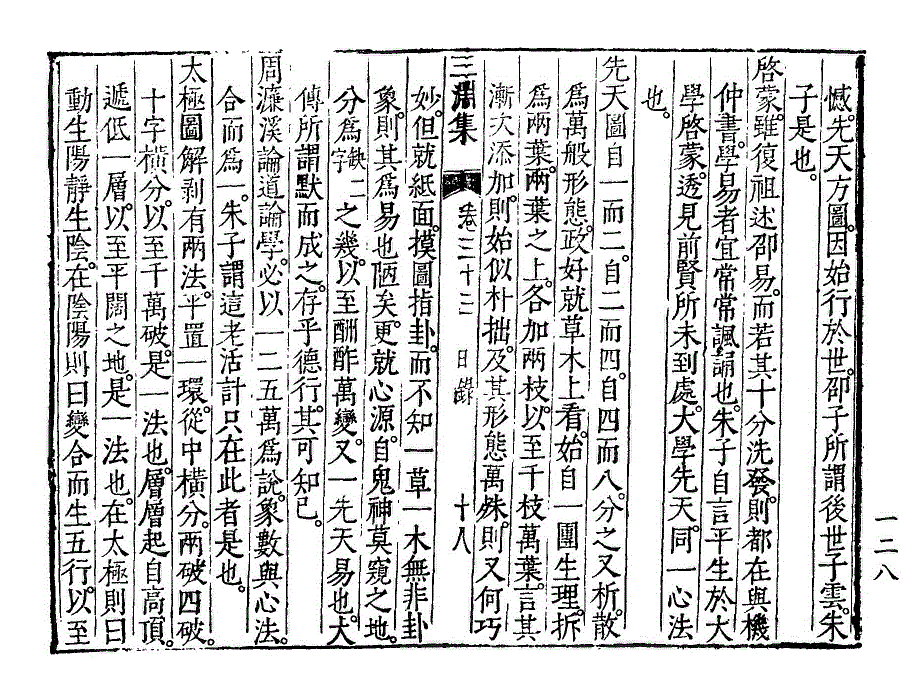 憾。先天方图。因始行于世。邵子所谓后世子云。朱子是也。
憾。先天方图。因始行于世。邵子所谓后世子云。朱子是也。启蒙。虽复祖述邵易。而若其十分洗发。则都在与机仲书。学易者宜常常讽诵也。朱子自言平生于大学启蒙。透见前贤所未到处。大学先天。同一心法也。
先天图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分之又析。散为万般形态。政好就草木上看。始自一团生理。拆为两叶。两叶之上。各加两枝。以至千枝万叶。言其渐次添加。则始似朴拙。及其形态万殊。则又何巧妙。但就纸面。摸图指卦。而不知一草一木无非卦象。则其为易也陋矣。更就心源。自鬼神莫窥之地。分为(缺二字)之几。以至酬酢万变。又一先天易也。大传所谓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其可知已。
周濂溪论道论学。必以一二五万为说。象数与心法。合而为一。朱子谓这老活计只在此者是也。
太极图解剥有两法。平置一环。从中横分。两破四破。十字横分。以至千万破。是一法也。层层起自高顶。递低一层。以至平阔之地。是一法也。在太极则曰动生阳静生阴。在阴阳则曰变合而生五行。以至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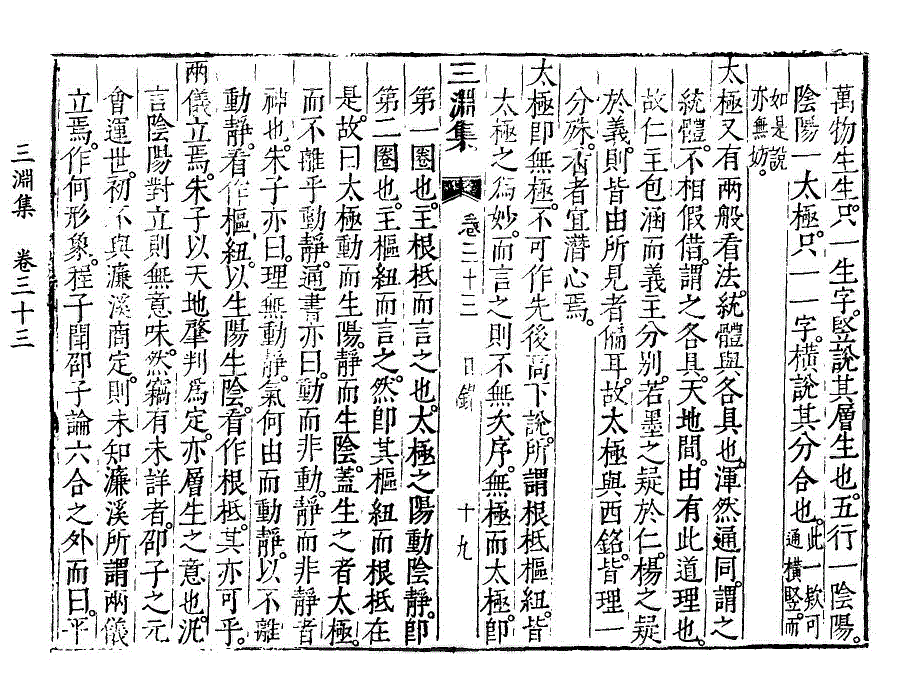 万物生生。只一生字。竖说其层生也。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只一一字。横说其分合也。(此一款可通横竖。而如是说亦无妨。)
万物生生。只一生字。竖说其层生也。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只一一字。横说其分合也。(此一款可通横竖。而如是说亦无妨。)太极又有两般看法。统体与各具也。浑然通同。谓之统体。不相假借。谓之各具。天地间。由有此道理也。故仁主包涵而义主分别。若墨之疑于仁。杨之疑于义。则皆由所见者偏耳。故太极与西铭。皆理一分殊。看者宜潜心焉。
太极即无极。不可作先后高下说。所谓根柢枢纽。皆太极之为妙。而言之则不无次序。无极而太极。即第一圈也。主根柢而言之也。太极之阳动阴静。即第二圈也。主枢纽而言之。然即其枢纽而根柢在是。故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盖生之者太极。而不离乎动静。通书亦曰。动而非动。静而非静者神也。朱子亦曰。理无动静。气何由而动静。以不离动静。看作枢纽。以生阳生阴。看作根柢。其亦可乎。
两仪立焉。朱子以天地肇判为定。亦层生之意也。汎言阴阳对立则无意味。然窃有未详者。邵子之元会运世。初不与濂溪商定。则未知濂溪所谓两仪立焉。作何形象。程子闻邵子论六合之外而曰。平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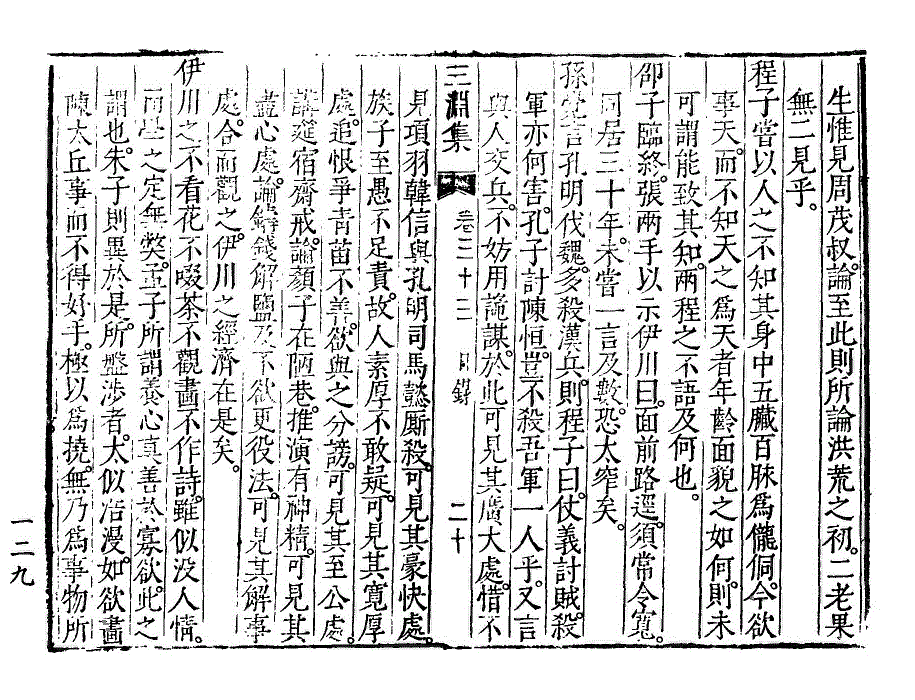 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则所论洪荒之初。二老果无二见乎。
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则所论洪荒之初。二老果无二见乎。程子尝以人之不知其身中五脏百脉为儱侗。今欲事天。而不知天之为天者年龄面貌之如何。则未可谓能致其知。两程之不语及何也。
邵子临终。张两手以示伊川曰。面前路径。须常令宽。同居三十年。未尝一言及数。恐太窄矣。
孙觉言孔明伐魏。多杀汉兵。则程子曰。仗义讨贼。杀军亦何害。孔子讨陈恒。岂不杀吾军一人乎。又言与人交兵。不妨用诡谋。于此可见其广大处。惜不见项羽韩信与孔明司马懿厮杀。可见其豪快处。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素厚不敢疑。可见其宽厚处。追恨争青苗不善。欲与之分谤。可见其至公处。讲筵宿斋戒。论颜子在陋巷。推演有神精。可见其尽心处。论铸钱解盐及不欲更役法。可见其解事处。合而观之。伊川之经济在是矣。
伊川之不看花不啜茶不观画不作诗。虽似没人情。而学之定无弊。孟子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之谓也。朱子则异于是。所盘涉者。太似浩漫。如欲画陈太丘事而不得好手。极以为挠。无乃为事物所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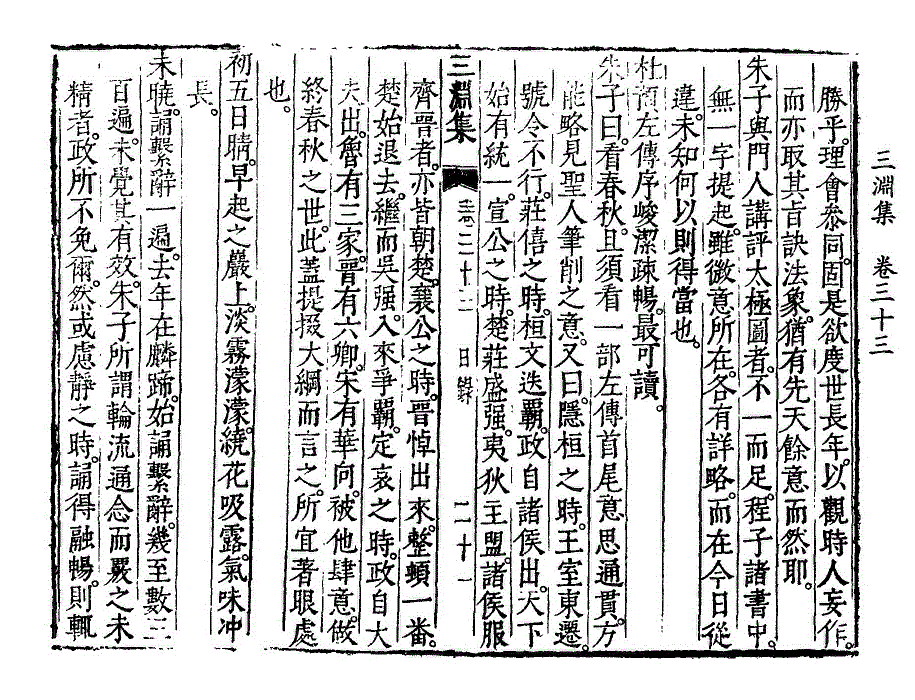 胜乎。理会参同。固是欲度世长年。以观时人妄作。而亦取其旨诀法象。犹有先天馀意而然耶。
胜乎。理会参同。固是欲度世长年。以观时人妄作。而亦取其旨诀法象。犹有先天馀意而然耶。朱子与门人讲评太极图者。不一而足。程子诸书中。无一字提起。虽微意所在。各有详略。而在今日从违。未知何以则得当也。
杜预左传序峻洁疏畅。最可读。
朱子曰。看春秋。且须看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之意。又曰。隐桓之时。王室东迁。号令不行。庄僖之时。桓文迭霸。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盛强。夷狄主盟。诸侯服齐晋者。亦皆朝楚。襄公之时。晋悼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强。入来争霸。定哀之时。政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此盖提掇大纲而言之。所宜著眼处也。
初五日
晴。早起之岩上。淡雾濛濛。绕花吸露。气味冲长。
未晓。诵系辞一遍。去年在麟蹄。始诵系辞。几至数三百遍。未觉其有效。朱子所谓轮流通念而覈之未精者。政所不免尔。然或虑静之时。诵得融畅。则辄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0L 页
 令胸襟洞豁。若有所得。诵书多矣。惟诵系辞为然。踏山川多矣。惟关北之行。似有开广之乐。
令胸襟洞豁。若有所得。诵书多矣。惟诵系辞为然。踏山川多矣。惟关北之行。似有开广之乐。溪流甚聒耳。恶之而欲其微则愈觉聒聒。以为佳声而与之吻合则未觉其喧闹。大学或问。同焉而不知其恶。阻焉而不知其善。政如此。盖阻则抵敌。同则浑沦故也。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历考古今。多有不然。温峤绝裾。而为晋平敦峻之乱则社稷臣也。王祥致冰鲤。而以魏三老。进玺于司马昭则负国人也。举其忠孝之特绝者而言之。尚如此。馀不可一一较也。然则孝不必忠。忠不必孝。固不可相通耶。且以耳目所睹记言之。居家以孝悌见称者。立朝多骫骳不振。岂慈良婉顺。宜于闺门而不宜于朝廷耶。盖朝廷是非之地。从违献替。不容一刻放过。未可以雍容循默支过。故必须武健者胜任。所以世所称孝子者。反不若在家多骨者之能济事也。然究极言之。为孝之道。岂止婉顺而已乎。父母有过。号泣以谏。至挞之流血而不弛者。乃为真孝。如王祥辈虽能致冰鲤黄雀。而未必为孰谏之事。朱子所以有死孝活孝之辨。虽诚切。如王祥。以其不学之故。止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1H 页
 于死孝。盖乌鸦之类。遍厚于慈一边者也。
于死孝。盖乌鸦之类。遍厚于慈一边者也。曾子为可。而被大杖几毙。受责于孔子。则惟大舜方为活孝。孝岂可易言哉。真能学问。道理通透。则孝于事瞽。忠于事尧。固无所不可。岂如一峤一祥之不可兼哉。若就气质上较量。则刚果疏通者。方可宜家宜国。柳公绰之类。庶几近之。
孝者百行之源。古有是言。盖举其本末表里而谓之孝也。今也见人之居家。稍子谅者。以为真孝。可兼众善。荐之于国。多露丑拙。此不可不审者也。孔子以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者。置在第二位者何也。盖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孝弟之大熟而能有作用者也。如高柴之泣血三年。而才短于为宰。则孔子谓贼夫人之子。若是者只可使处乡党而已。孔子所以语子贡者。凡有四层。使于四方为上层。称孝称弟为第二。言必信行必果为第三。斗筲之辈。为最下层。
余尝以人品六等。排定位次。每为后学切切言之。以为惩劝之准。
第一位圣人。一疵不存。万理明尽。
第二位大贤。道全德备。守而未化。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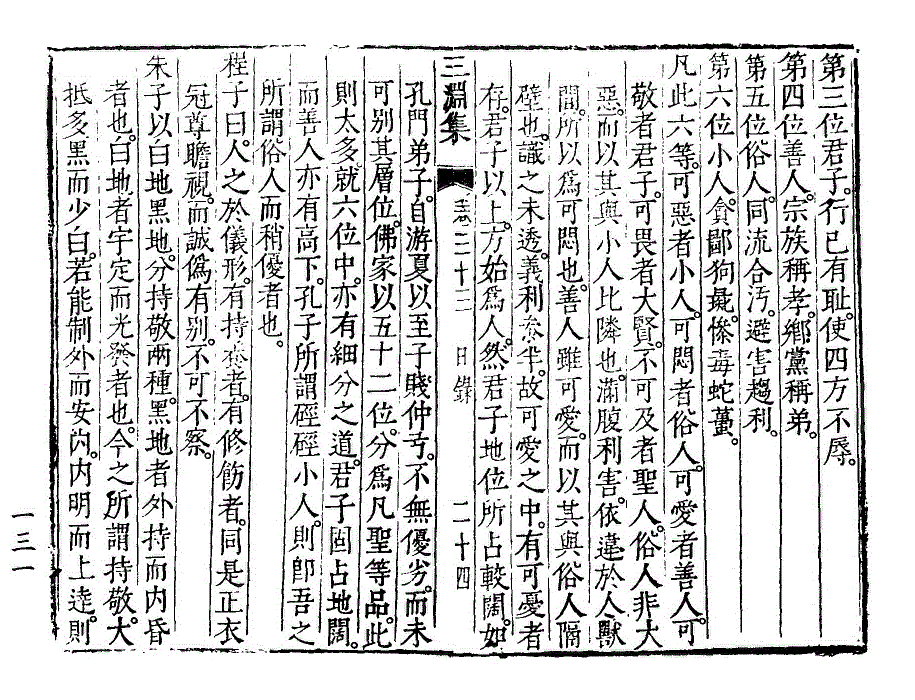 第三位君子。行己有耻。使四方不辱。
第三位君子。行己有耻。使四方不辱。第四位善人。宗族称孝。乡党称弟。
第五位俗人。同流合污。避害趋利。
第六位小人。贪鄙狗彘。惨毒蛇虿。
凡此六等。可恶者小人。可闷者俗人。可爱者善人。可敬者君子。可畏者大贤。不可及者圣人。俗人非大恶。而以其与小人比邻也。满腹利害。依违于人,兽间。所以为可闷也。善人虽可爱。而以其与俗人隔壁也。识之未透。义利参半。故可爱之中。有可忧者存。君子以上。方始为人。然君子地位所占较阔。如孔门弟子。自游夏以至子贱仲弓。不无优劣。而未可别其层位。佛家以五十二位。分为凡圣等品。此则太多。就六位中。亦有细分之道。君子固占地阔。而善人亦有高下。孔子所谓硁硁小人。则即吾之所谓俗人而稍优者也。
程子曰。人之于仪形。有持养者。有修饬者。同是正衣冠尊瞻视。而诚伪有别。不可不察。
朱子以白地黑地。分持敬两种。黑地者外持而内昏者也。白地者宇定而光发者也。今之所谓持敬。大抵多黑而少白。若能制外而安内。内明而上达。则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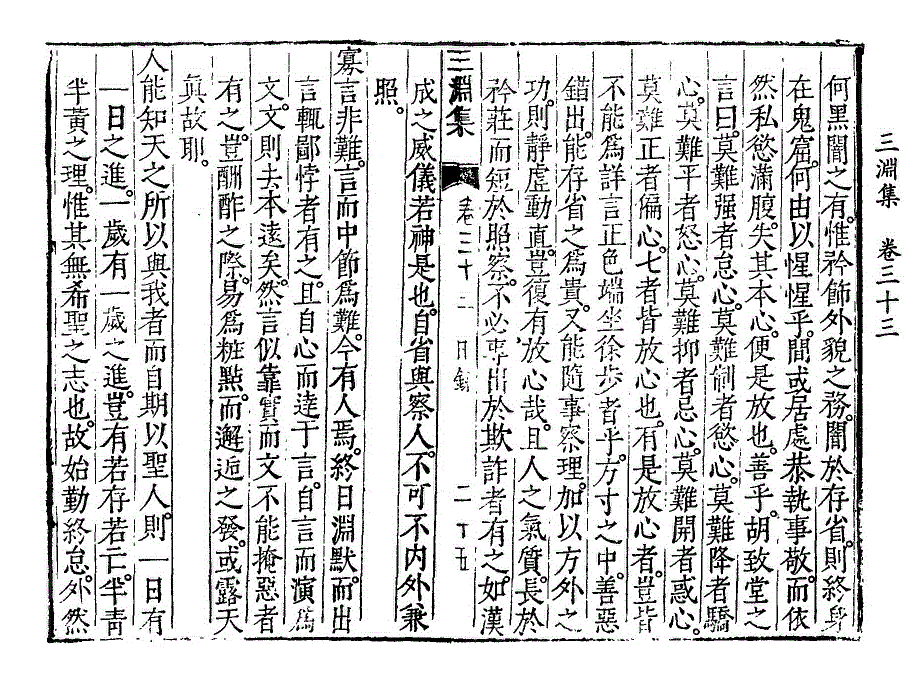 何黑闇之有。惟矜饰外貌之务。闇于存省。则终身在鬼窟。何由以惺惺乎。间或居处恭执事敬。而依然私欲满腹。失其本心。便是放也。善乎。胡致堂之言曰。莫难强者怠心。莫难制者欲心。莫难降者骄心。莫难平者怒心。莫难抑者忌心。莫难开者惑心。莫难正者偏心。七者皆放心也。有是放心者。岂皆不能为详言正色端坐徐步者乎。方寸之中。善恶错出。能存省之为贵。又能随事察理。加以方外之功。则静虚动直。岂复有放心哉。且人之气质。长于矜庄而短于照察。不必专出于欺诈者有之。如汉成之威仪若神是也。自省与察人。不可不内外兼照。
何黑闇之有。惟矜饰外貌之务。闇于存省。则终身在鬼窟。何由以惺惺乎。间或居处恭执事敬。而依然私欲满腹。失其本心。便是放也。善乎。胡致堂之言曰。莫难强者怠心。莫难制者欲心。莫难降者骄心。莫难平者怒心。莫难抑者忌心。莫难开者惑心。莫难正者偏心。七者皆放心也。有是放心者。岂皆不能为详言正色端坐徐步者乎。方寸之中。善恶错出。能存省之为贵。又能随事察理。加以方外之功。则静虚动直。岂复有放心哉。且人之气质。长于矜庄而短于照察。不必专出于欺诈者有之。如汉成之威仪若神是也。自省与察人。不可不内外兼照。寡言非难。言而中节为难。今有人焉。终日渊默。而出言辄鄙悖者有之。且自心而达于言。自言而演为文。文则去本远矣。然言似靠实而文不能掩恶者有之。岂酬酢之际。易为妆点。而邂逅之发。或露天真故耶。
人能知天之所以与我者而自期以圣人。则一日有一日之进。一岁有一岁之进。岂有若存若亡。半青半黄之理。惟其无希圣之志也。故始勤终怠。外然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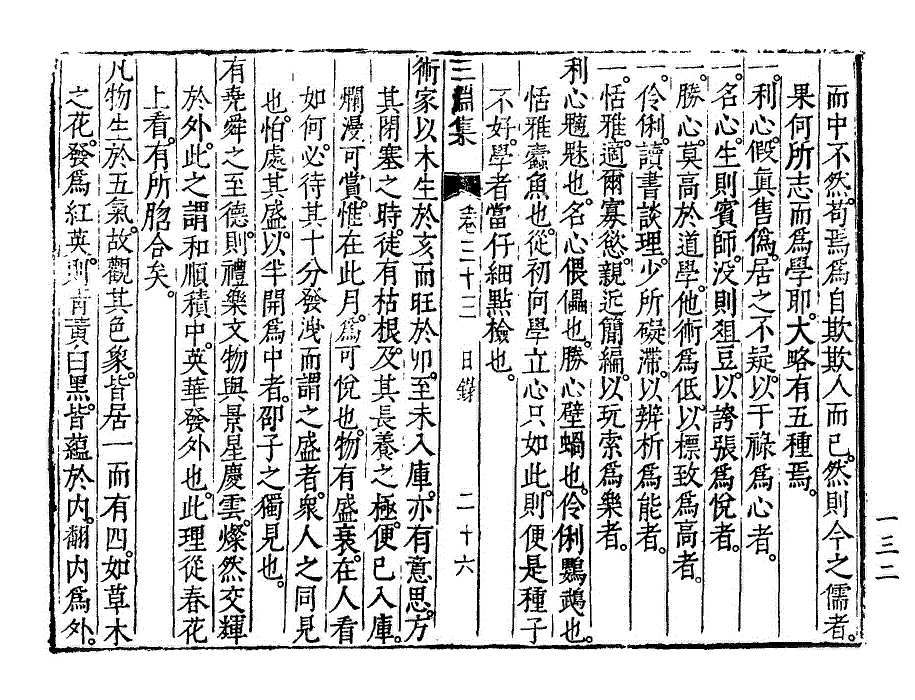 而中不然。苟焉为自欺欺人而已。然则今之儒者。果何所志而为学耶。大略有五种焉。
而中不然。苟焉为自欺欺人而已。然则今之儒者。果何所志而为学耶。大略有五种焉。一。利心。假真售伪。居之不疑。以干禄为心者。
一。名心。生则宾师。没则俎豆。以誇张为悦者。
一。胜心。莫高于道学。他术为低。以标致为高者。
一。伶俐。读书谈理。少所碍滞。以辨析为能者。
一。恬雅。适尔寡欲。亲近简编。以玩索为乐者。
利心魑魅也。名心偎儡也。胜心壁蜗也。伶俐鹦鹉也。恬雅蠹鱼也。从初向学立心只如此。则便是种子不好。学者当仔细点检也。
术家以木生于亥而旺于卯。至未入库。亦有意思。方其闭塞之时。徒有枯根。及其长养之极。便已入库。烂漫可赏。惟在此月。为可悦也。物有盛衰。在人看如何。必待其十分发泄而谓之盛者。众人之同见也。怕处其盛。以半开为中者。邵子之独见也。
有尧舜之至德。则礼乐文物与景星庆云。灿然交辉于外。此之谓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也。此理从春花上看。有所吻合矣。
凡物生于五气。故观其色象。皆居一而有四。如草木之花。发为红英。则青黄白黑。皆蕴于内。翻内为外。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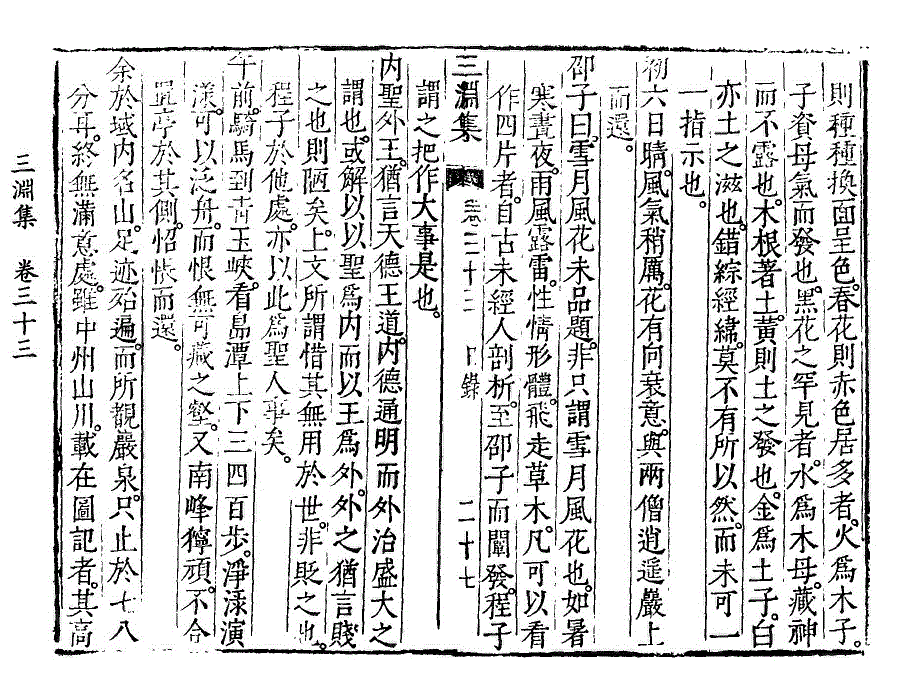 则种种换面呈色。春花则赤色居多者。火为木子。子资母气而发也。黑花之罕见者。水为木母。藏神而不露也。木根著土。黄则土之发也。金为土子。白亦土之滋也。错综经纬。莫不有所以然。而未可一一指示也。
则种种换面呈色。春花则赤色居多者。火为木子。子资母气而发也。黑花之罕见者。水为木母。藏神而不露也。木根著土。黄则土之发也。金为土子。白亦土之滋也。错综经纬。莫不有所以然。而未可一一指示也。初六日
晴。风气稍厉。花有向衰意。与两僧逍遥岩上而还。
邵子曰。雪月风花未品题。非只谓雪月风花也。如暑寒昼夜。雨风露雷。性情形体。飞走草木。凡可以看作四片者。自古未经人剖析。至邵子而阐发。程子谓之把作大事是也。
内圣外王。犹言天德王道。内德通明而外治盛大之谓也。或解以以圣为内而以王为外。外之犹言贱之也则陋矣。上文所谓惜其无用于世。非贬之也。程子于他处。亦以此为圣人事矣。
午前。骑马到青玉峡。看岛潭上下三四百步。净渌演漾。可以泛舟。而恨无可藏之壑。又南峰狞顽。不合置亭于其侧。怊怅而还。
余于域内名山。足迹殆遍。而所睹岩泉。只止于七八分耳。终无满意处。虽中州山川。载在图记者。其高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3L 页
 下饶乏。亦可坐料。黄山华岳。以岩峦为胜。而涧壑则缺。庐山雁宕。渊瀑称壮。而峰岭稍低。大者如此。馀可类知。然则等山川于人物。终无圣位之可拟乎。意者成质于地。固宜滞局偏胜。不能如最灵参三者备众善而极纯粹也。其理果如此否。
下饶乏。亦可坐料。黄山华岳。以岩峦为胜。而涧壑则缺。庐山雁宕。渊瀑称壮。而峰岭稍低。大者如此。馀可类知。然则等山川于人物。终无圣位之可拟乎。意者成质于地。固宜滞局偏胜。不能如最灵参三者备众善而极纯粹也。其理果如此否。李延平居室。不作费心事。衰晚之人。切宜师法。
朱子武夷距五夫里不满百里。而犹曰无力可往来。又曰。近处无山。随分占取。则余之来往雪岳。可谓不量力矣。
朱子以越中山水为浅狭。所占武夷。亦曰不甚好。窃想其形局峻隘不宽平。使游者无夷旷意思。故不甚惬尚也。然则山不必纯石无寸土而后。可以称奇。使朱子观皆骨。必病其太隘。如万瀑九渊之间。逼窄无容足处。岂能如玉渊三峡宏雄壮丽乎。金刚决不及庐山。以峰峦论之。安可望太华黄山乎。攀提裁著脚度。可在五六等矣。
诗亡然后春秋作。所谓诗亡者。一则列国有诗。而天子不采以行黜陟也。一则天子治内。有风而无雅也。论王风者。以为雅变而为风者恐未然。风有风体。雅有雅体。非但列国有风。天子畿内。亦自有风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4H 页
 与大小雅并行。而及其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朝廷之上。亦无所受釐陈戒。则大小雅亡。而所馀者风。如黍离是已。风自有体。岂变调而为雅乎。
与大小雅并行。而及其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朝廷之上。亦无所受釐陈戒。则大小雅亡。而所馀者风。如黍离是已。风自有体。岂变调而为雅乎。列国之风。天子之所采以黜陟也。天子之风。采以自考其治忽。势所固然。周南即文王三分有二之时。则便是天子风也。诗序国史之说最乱道。至以关雎为追作。则全无活意。便是诗亡矣。程子云诗大率后人追作。未看破诗序故也。
硕人之诗。在东迁之后。而不为天子所采。则非诗之亡。天子之政亡也。
声音之道。与政相通。诗教之不行。便是天子无政。故孔子不得不作春秋。感麟而作。与经成而麟至。有两说。杜预以为始于麟至。终于麟亡者得之矣。
诗则一也。删前删后。虽言志葩藻之有别。而以温柔敦厚为旨。以玲珑掩映为格。则古今同然。程子不解今诗。故所释风雅。率多牵强扭捏。不能如朱子之脱洒。故其解蒹葭诗。切切以刈蒹作蚕箔事。著实疏释。依以讽诵。如吃木札。朱子于此。奋然以秋水方盛之时。破题而活泼释去。一似九歌中湘君湘夫人散声。快哉快哉。朱子自少用功于诗。源流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4L 页
 洞彻。故能如是善解。其释兴体。以则矣二字提掇。亦有妙理。如是而后。可免固哉之诮矣。
洞彻。故能如是善解。其释兴体。以则矣二字提掇。亦有妙理。如是而后。可免固哉之诮矣。兴体有两般。如以雎鸠兴淑女。以麟兴公子。则意近于比。如隰苓山榛之类。乃无端触兴而起。非谓其衬切也。朱子谓兴之不衬者。意味尤深长。真个如此。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读之有绕梁之音。诗其可知已。
大学治国章三引诗。令人手舞足蹈。文亦诗也。诗亦乐也。生今之世。不闻古乐。只合于此等处。涵畅而歆动之。庶有进步尔。
初七日
朝气料峭。不欲开户。尝思光风霁月。最是难得。光者清和之谓。稍带峭厉凝涩则非也。霁即澄朗之谓。乍有纤氛微翳则非也。宋玉所谓光风转蕙泛崇兰。谢庄所谓升清质降澄晖。以十分言之也。须是十分洒落。方可谓之光霁。就人心上而验之。乍见欲寡过少。可拟于光霁。而犹有放不下融未尽者。则未可谓洒落。或至事有难处。交战于中。牵制惹绊。殊未快活。自谓舍东趣西而未免有骑墙意思。则亦何能彷佛于光霁乎。山谷以此形容周濂溪胸次。最善名状。延平则持作话头。要令学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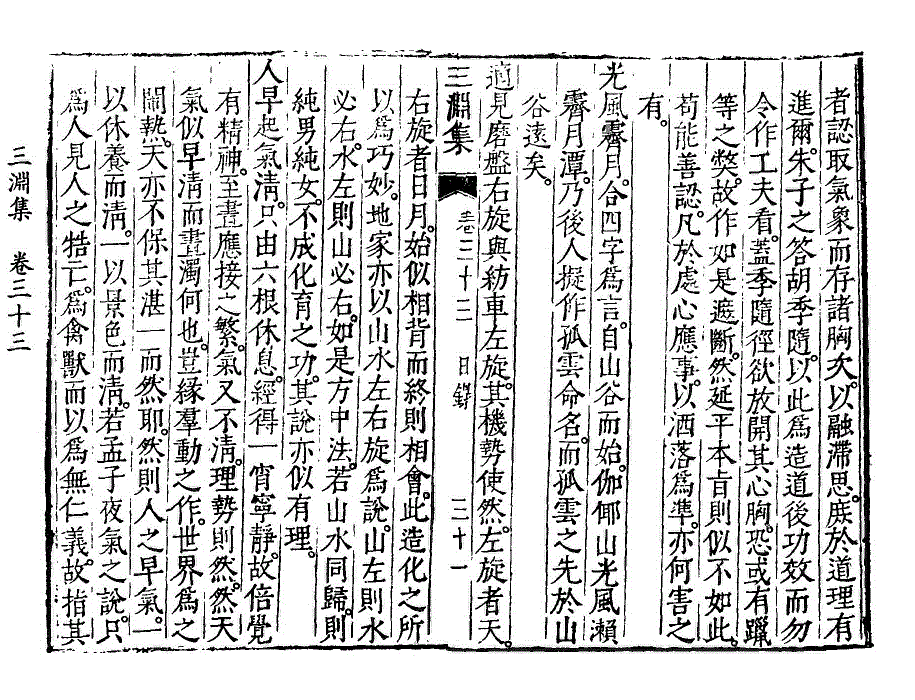 者认取气象而存诸胸次。以融滞思。庶于道理有进尔。朱子之答胡季随。以此为造道后功效而勿令作工夫看。盖季随径欲放开其心胸。恐或有躐等之弊。故作如是遮断。然延平本旨则似不如此。苟能善认。凡于处心应事。以洒落为准。亦何害之有。
者认取气象而存诸胸次。以融滞思。庶于道理有进尔。朱子之答胡季随。以此为造道后功效而勿令作工夫看。盖季随径欲放开其心胸。恐或有躐等之弊。故作如是遮断。然延平本旨则似不如此。苟能善认。凡于处心应事。以洒落为准。亦何害之有。光风霁月。合四字为言。自山谷而始。伽倻山光风濑霁月潭。乃后人拟作孤云命名。而孤云之先于山谷远矣。
适见磨盘右旋与纺车左旋。其机势使然。左旋者天。右旋者日月。始似相背而终则相会。此造化之所以为巧妙。地家亦以山水左右旋为说。山左则水必右。水左则山必右。如是方中法。若山水同归。则纯男纯女。不成化育之功。其说亦似有理。
人早起气清。只由六根休息。经得一宵宁静。故倍觉有精神。至昼应接之繁。气又不清。理势则然。然天气似早清而昼浊何也。岂缘群动之作。世界为之闹热。天亦不保其湛一而然耶。然则人之早气。一以休养而清。一以景色而清。若孟子夜气之说。只为人见人之牿亡。为禽兽而以为无仁义。故指其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5L 页
 休养时湛然者而言之曰。此气之存。宛然与人相近云尔。至其著功。要欲克去人欲。回昼气为朝气尔。初非谓俟其夜气之至。挹其清淑以受用。如道家觅先天真一之谓也。今之讲牛山章者。槩未免此。延平所解。亦微有漏逗者尔。
休养时湛然者而言之曰。此气之存。宛然与人相近云尔。至其著功。要欲克去人欲。回昼气为朝气尔。初非谓俟其夜气之至。挹其清淑以受用。如道家觅先天真一之谓也。今之讲牛山章者。槩未免此。延平所解。亦微有漏逗者尔。孙子兵法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三时之气。固自不同。然敌人相对同值一时。未知用何术而使我气常朝。而彼气常昼乎。如刘锜顺昌之战。政当暑热。兀朮之军。再鼓气衰。疲顿于城外。而我军则更番迭出。新出者皆从凉处。服清暑茶汤而跃出。故气健而战猛。以一当十。此所谓避其朝气。击其惰气者也。
横渠谓夙兴干事。良由人气清则勤不得閒。伊川谓若此则是专为气所使。横渠谓此则自然。终觉伊川说忒高。
栗谷所谓善者清气之发。恶者浊气之发。徒知主张者在气。而不以性善为重。亦异乎孟子矣。且发之为言。蓦然发出之谓也。如所谓乍见赤子之入井是已。当其时。凡圣慈暴一色。善情之发。目击而颡泚。何清浊之可拘哉。仲氏之言曰。气至清者。绝无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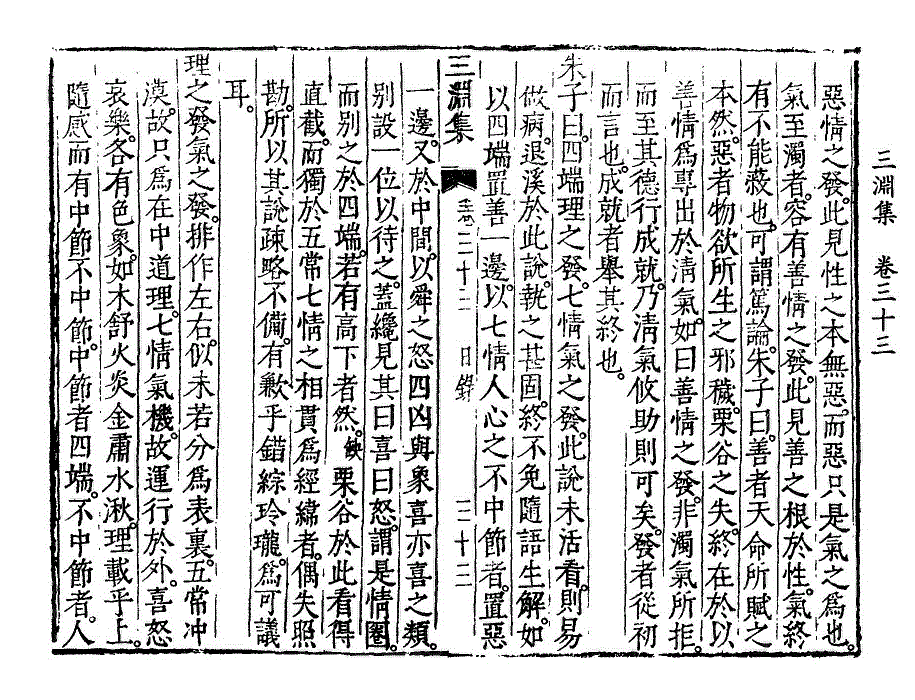 恶情之发。此见性之本无恶。而恶只是气之为也。气至浊者。容有善情之发。此见善之根于性。气终有不能蔽也。可谓笃论。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赋之本然。恶者物欲所生之邪秽。栗谷之失。终在于以善情为专出于清气。如曰善情之发。非浊气所拒。而至其德行成就。乃清气攸助则可矣。发者从初而言也。成就者举其终也。
恶情之发。此见性之本无恶。而恶只是气之为也。气至浊者。容有善情之发。此见善之根于性。气终有不能蔽也。可谓笃论。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赋之本然。恶者物欲所生之邪秽。栗谷之失。终在于以善情为专出于清气。如曰善情之发。非浊气所拒。而至其德行成就。乃清气攸助则可矣。发者从初而言也。成就者举其终也。朱子曰。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此说未活看。则易做病。退溪于此说。执之甚固。终不免随语生解。如以四端置善一边。以七情人心之不中节者。置恶一边。又于中间。以舜之怒四凶与象喜亦喜之类。别设一位以待之。盖才见其曰喜曰怒。谓是情圈。而别之于四端。若有高下者然。(缺)栗谷于此看得直截。而独于五常七情之相贯为经纬者。偶失照勘。所以其说疏略不备。有歉乎错综玲珑。为可议耳。
理之发气之发。排作左右。似未若分为表里。五常冲漠。故只为在中道理。七情气机。故运行于外。喜怒哀乐。各有色象。如木舒火炎金肃水湫。理载乎上。随感而有中节不中节。中节者四端。不中节者。人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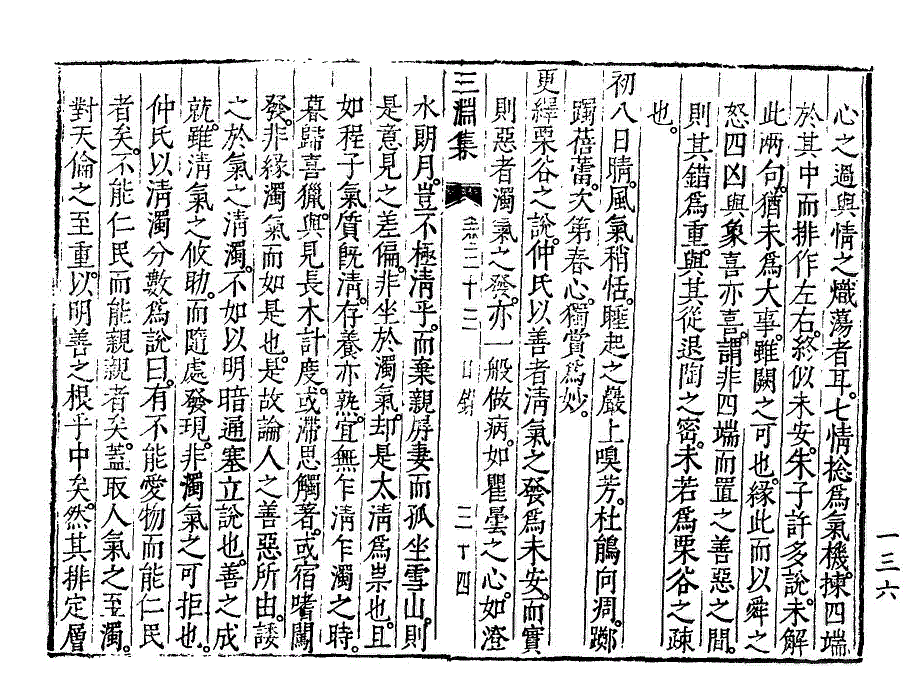 心之过与情之炽荡者耳。七情总为气机。拣四端于其中而排作左右。终似未安。朱子许多说。未解此两句。犹未为大事。虽阙之可也。缘此而以舜之怒四凶与象喜亦喜。谓非四端而置之善恶之间。则其错为重。与其从退陶之密。未若为栗谷之疏也。
心之过与情之炽荡者耳。七情总为气机。拣四端于其中而排作左右。终似未安。朱子许多说。未解此两句。犹未为大事。虽阙之可也。缘此而以舜之怒四凶与象喜亦喜。谓非四端而置之善恶之间。则其错为重。与其从退陶之密。未若为栗谷之疏也。初八日
晴。风气稍恬。睡起之岩上嗅芳。杜鹃向凋。踯躅蓓蕾。次第春心。独赏为妙。
更绎栗谷之说。仲氏以善者清气之发为未安。而实则恶者浊气之发。亦一般做病。如瞿昙之心。如澄水朗月。岂不极清乎。而弃亲屏妻而孤坐雪山。则是意见之差偏。非坐于浊气。却是太清为祟也。且如程子气质既清。存养亦熟。宜无乍清乍浊之时。暮归喜猎。与见长木计度。或滞思触著。或宿嗜闯发。非缘浊气而如是也。是故论人之善恶所由。诿之于气之清浊。不如以明暗通塞立说也。善之成就。虽清气之攸助。而随处发现。非浊气之可拒也。仲氏以清浊分数为说曰。有不能爱物而能仁民者矣。不能仁民而能亲亲者矣。盖取人气之至浊。对天伦之至重。以明善之根乎中矣。然其排定层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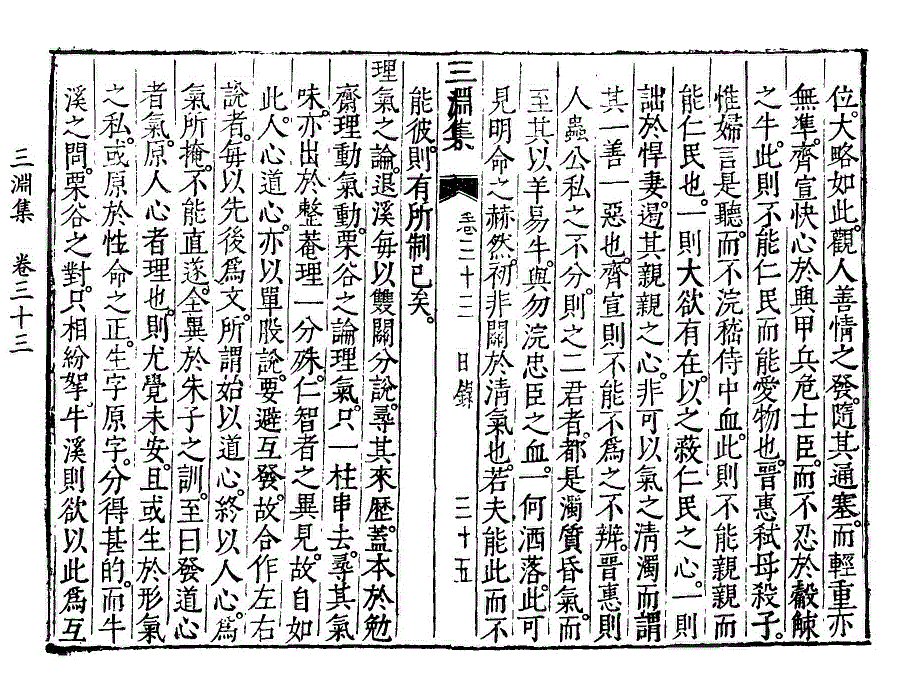 位。大略如此。观人善情之发。随其通塞。而轻重亦无准。齐宣快心于兴甲兵危士臣。而不忍于觳觫之牛。此则不能仁民而能爱物也。晋惠弑母杀子。惟妇言是听。而不浣嵇侍中血。此则不能亲亲而能仁民也。一则大欲有在。以之蔽仁民之心。一则诎于悍妻。遏其亲亲之心。非可以气之清浊而谓其一善一恶也。齐宣则不能不为之不辨。晋惠则人虫公私之不分。则之二君者。都是浊质昏气。而至其以羊易牛。与勿浣忠臣之血。一何洒落。此可见明命之赫然。初非关于清气也。若夫能此而不能彼。则有所制已矣。
位。大略如此。观人善情之发。随其通塞。而轻重亦无准。齐宣快心于兴甲兵危士臣。而不忍于觳觫之牛。此则不能仁民而能爱物也。晋惠弑母杀子。惟妇言是听。而不浣嵇侍中血。此则不能亲亲而能仁民也。一则大欲有在。以之蔽仁民之心。一则诎于悍妻。遏其亲亲之心。非可以气之清浊而谓其一善一恶也。齐宣则不能不为之不辨。晋惠则人虫公私之不分。则之二君者。都是浊质昏气。而至其以羊易牛。与勿浣忠臣之血。一何洒落。此可见明命之赫然。初非关于清气也。若夫能此而不能彼。则有所制已矣。理气之论。退溪每以双关分说。寻其来历。盖本于勉斋理动气动。栗谷之论理气。只一柱串去。寻其气味。亦出于整庵理一分殊。仁智者之异见。故自如此。人心道心。亦以单股说。要避互发。故合作左右说者。每以先后为文。所谓始以道心。终以人心。为气所掩。不能直遂。全异于朱子之训。至曰发道心者气。原人心者理也。则尤觉未安。且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生字原字。分得甚的。而牛溪之问。栗谷之对。只相纷挐。牛溪则欲以此为互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7L 页
 发之證。已是不衬。栗谷亦未能明白辨破。费了数多简札。有歉于相悦以解。只形气二字。初未咬破故也。窃谓气之对理者。凡有三个。气质也气机也形气也。气质有偏局。则对本然而言也。气机有妄动。则对中节而言也。形气易自私。则对性命而言也。言之。须从律令。而今乃浑而一之。方论互发。不以气机为说。而至论人心。又舍形气为说。所以言愈多。理未晢。是为可议之大者尔。栗谷深避互发之说。到底不以双关立说。始与牛溪言。峻塞其理气对说矣。终被逼拶。乃从其理为主气为主之说。未知整庵见之。以为如何。
发之證。已是不衬。栗谷亦未能明白辨破。费了数多简札。有歉于相悦以解。只形气二字。初未咬破故也。窃谓气之对理者。凡有三个。气质也气机也形气也。气质有偏局。则对本然而言也。气机有妄动。则对中节而言也。形气易自私。则对性命而言也。言之。须从律令。而今乃浑而一之。方论互发。不以气机为说。而至论人心。又舍形气为说。所以言愈多。理未晢。是为可议之大者尔。栗谷深避互发之说。到底不以双关立说。始与牛溪言。峻塞其理气对说矣。终被逼拶。乃从其理为主气为主之说。未知整庵见之。以为如何。初九日
晴有风。食后之屋北田。看斗奴播耳麦。仍思农之为利。不可胜量。凡言利者皆以同甲为准。同甲者倍售也。如种粟良田。一升之收。得二十斗。则便是百同甲也。工商百业。无可比拟。又以民风言之。归之南亩。则桀黠化为淳厖。纳诸工商。则淳谨化为巧诈。可知术不可不慎也。东俗百事草率。至于农务。亦未竭智尽法。一则不事粪田。一则立苗不疏。一则不解壅本。一则锄治卤莽。以是而望大穫。如未副望。则以岁为罪。甚可憎。周礼粪田之法。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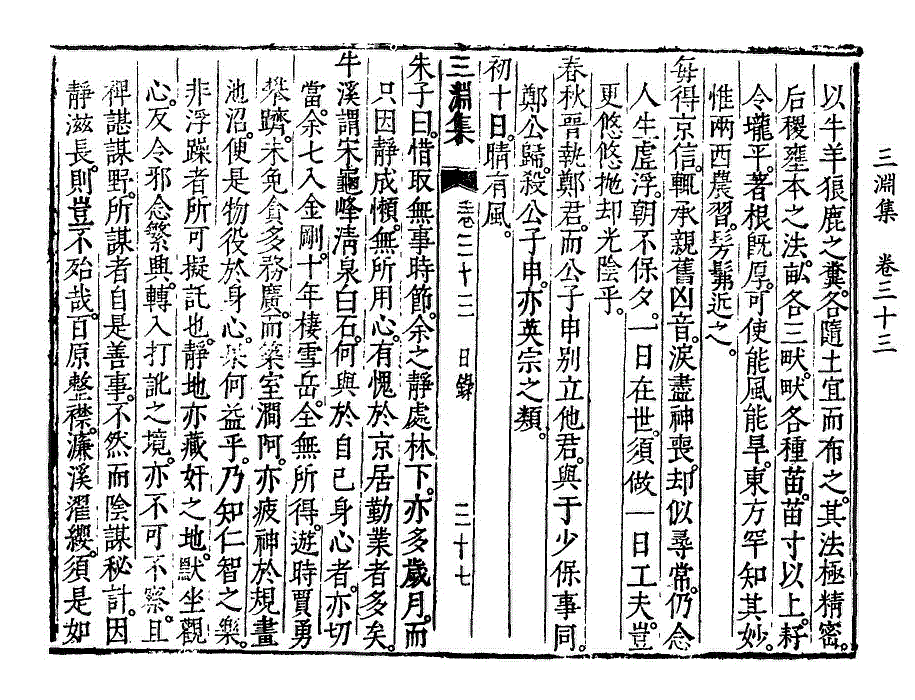 以牛羊狼鹿之粪。各随土宜而布之。其法极精密。后稷壅本之法。亩各三畎。畎各种苗。苗寸以上。耔令垄平。著根既厚。可使能风能旱。东方罕知其妙。惟两西农习。髣髴近之。
以牛羊狼鹿之粪。各随土宜而布之。其法极精密。后稷壅本之法。亩各三畎。畎各种苗。苗寸以上。耔令垄平。著根既厚。可使能风能旱。东方罕知其妙。惟两西农习。髣髴近之。每得京信。辄承亲旧凶音。泪尽神丧。却似寻常。仍念人生虚浮。朝不保夕。一日在世。须做一日工夫。岂更悠悠抛却光阴乎。
春秋晋执郑君。而公子申别立他君。与于少保事同。郑公归。杀公子申。亦英宗之类。
初十日
晴有风。
朱子曰。惜取无事时节。余之静处林下。亦多岁月。而只因静成懒。无所用心。有愧于京居勤业者多矣。
牛溪谓宋龟峰清泉白石。何与于自己身心者。亦切当。余七入金刚。十年栖雪岳。全无所得。游时贾勇攀跻。未免贪多务广。而筑室涧阿。亦疲神于规画池沼。便是物役于身心。果何益乎。乃知仁智之乐。非浮躁者所可拟托也。静地亦藏奸之地。默坐观心。反令邪念繁兴。转入打讹之境。亦不可不察。且裨谌谋野。所谋者自是善事。不然而阴谋秘计。因静滋长。则岂不殆哉。百原整襟。濂溪濯缨。须是如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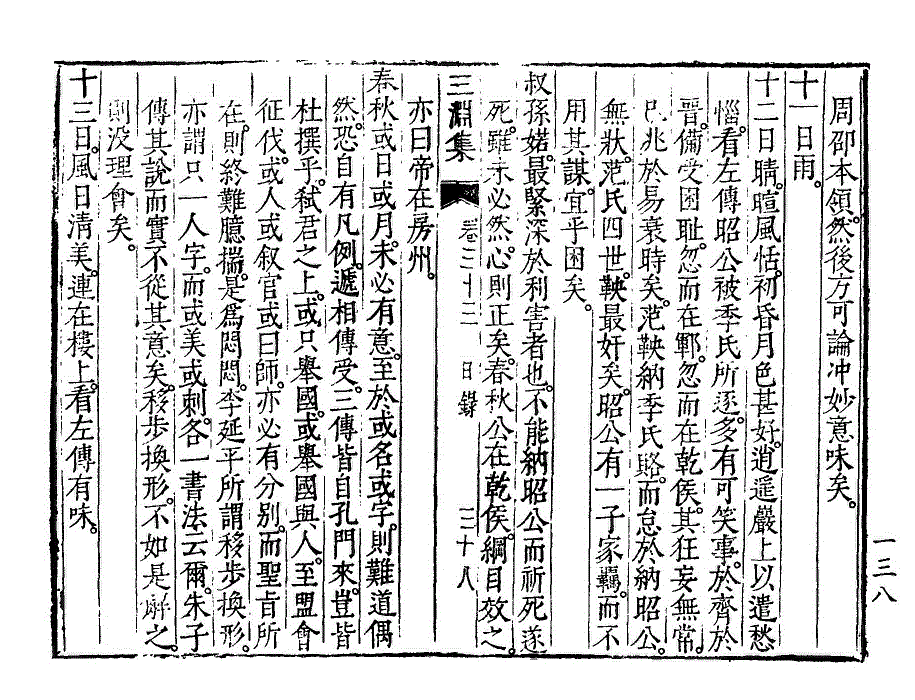 周邵本领。然后方可论冲妙意味矣。
周邵本领。然后方可论冲妙意味矣。十一日
雨。
十二日
晴。暄风恬。初昏月色甚好。逍遥岩上以遣愁恼。看左传昭公被季氏所逐。多有可笑事。于齐于晋。备受困耻。忽而在郓。忽而在乾侯。其狂妄无常。已兆于易衰时矣。范鞅纳季氏赂。而怠于纳昭公。无状。范氏四世。鞅最奸矣。昭公有一子家羁。而不用其谋。宜乎困矣。
叔孙婼。最紧深于利害者也。不能纳昭公而祈死遂死。虽未必然。心则正矣。春秋公在乾侯。纲目效之。亦曰帝在房州。
春秋或日或月。未必有意。至于或名或字。则难道偶然。恐自有凡例。递相传受。三传皆自孔门来。岂皆杜撰乎。弑君之上。或只举国。或举国与人。至盟会征伐。或人或叙官或曰师。亦必有分别。而圣旨所在。则终难臆揣。是为闷闷。李延平所谓移步换形。亦谓只一人字。而或美或刺。各一书法云尔。朱子传其说而实不从其意矣。移步换形。不如是解之。则没理会矣。
十三日
风日清美。连在楼上。看左传有味。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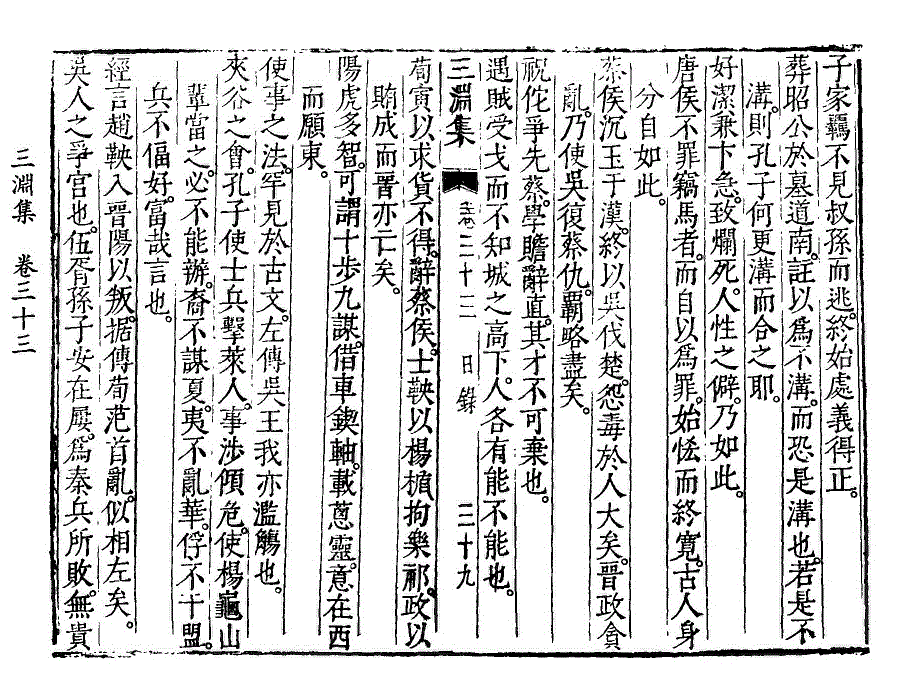 子家羁不见叔孙而逃。终始处义得正。
子家羁不见叔孙而逃。终始处义得正。葬昭公于墓道南。注以为不沟。而恐是沟也。若是不沟。则孔子何更沟而合之耶。
好洁兼卞急。致烂死。人性之僻。乃如此。
唐侯不罪窃马者。而自以为罪。始吝而终宽。古人身分自如此。
蔡侯沉玉于汉。终以吴伐楚。怨毒于人大矣。晋政贪乱。乃使吴复蔡仇。霸略尽矣。
祝佗争先蔡。学赡辞直。其才不可弃也。
遇贼受戈而不知城之高下。人各有能不能也。
荀寅以求货不得。辞蔡侯。士鞅以杨楯拘乐祁。政以贿成而晋亦亡矣。
阳虎多智。可谓十步九谋。借车锲轴。载葱灵。意在西而愿东。
使事之法。罕见于古文。左传吴王我亦滥觞也。
夹谷之会。孔子使士兵击莱人。事涉倾危。使杨龟山辈当之。必不能办。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富哉言也。
经言赵鞅入晋阳以叛。据传荀范首乱。似相左矣。
吴人之争宫也。伍胥孙子安在屡。为秦兵所败。无贵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39L 页
 有将略也。
有将略也。改步改玉。后来用之。主客似换。
定公之登武子台。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费人。亦危矣。
蒯聩始见郑师而惧。王良谓之妇人。而及救简子。再败郑师。亦猛将也。
程子以子路之死于孔悝。谓有商量处。义不使之拒父。而恐未然。以论语有是迂也之说观之。只欲与辄做事。盖得国而治。乃其素蕴。故苟于去就。不能如颜子用行舍藏。而亦有愧于疏疏浴沂者也。
十四日
洒雨又多风。朝上楼上。看左传。
救火郑鲁事。叙各不同。要皆有从容整暇之意。孔子曰。其桓僖乎。亲尽而庙不毁故也。
王生之荐张柳朔。则好不废过。恶不去善。柳朔则曰。王生授我矣。遂死于柏人。一则公。一则侠。
鲍牧始则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折其齿乎。而终则曰。谁非君之子。摇漾如此。宜乎及也。
泰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以泰伯仲雍分为二致。似有传说而然也。
卒三百人。有若与焉。盖将宵攻吴王。壮矣。冉求与樊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40H 页
 迟能拒齐师。子贡亦辩折吴人。孔门弟子之盛。有关于安危如此。诚异乎今之腐儒矣。
迟能拒齐师。子贡亦辩折吴人。孔门弟子之盛。有关于安危如此。诚异乎今之腐儒矣。孔子欲讨陈成子。而子路,子贡。或与陈瓘通款。或与成子接谈。似欠严正意。虽出于庇鲁。终有未快者矣。
子羔曰。不及。不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避难。以两说看之。子羔较黠矣。
吴人藩卫侯时。子贡语之太宰嚭。尽有口才。
公孙夏歌虞殡。陈子行具含玉。令人发立。
孟之反不伐。比之于赵鞅,蒯聩之各言上也。不翅贤矣。
十五日
晴。
左传叔孙豹事。最奇怪。与萧绎都江陵相似。一则为梦欺。一则为卜欺。然叔孙则三日不食。神明亦告之矣。
鲁昭三易衰而能于习仪。亦可异。自晋侯以为知礼。宜乎陈司败之问于孔子也。
晏婴学问不草草。其论和同之辨及以礼定国祝史不祈等处。可见其精透。子产尤深博论。伯有有鬼。使为之归。可谓知鬼神之情状。论晋侯病情亦透。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40L 页
 叔向则似无此等学识。只是刚直。三数叔鱼之恶。全没私情。
叔向则似无此等学识。只是刚直。三数叔鱼之恶。全没私情。十六日
晴。
左传观乾象。全以岁星周复为占。其法多难解。子产之占。楚灵之凶。只以周年判断矣。
单子之视下言徐。郑伯之视流行速之类。当时相者。能以此判其死生。而在今有不可必者。盖古人则威仪举止。夫人皆能检制如法。而一有不然。便是凶兆故也。今则人皆放倒。虽袒裼裸裎。未必为夭法也。
春秋虽辞简义晦。然包括则广。礼乐刑政。风雨雷露。草木虫鱼。日月星辰。年谷丰凶。举在其中。马迁所谓万物散殊。皆在春秋。是之谓也。吕伯恭教人。舍论语而先左传。则固为偏也。以为见之于行事之深切云。则亦有意思。读论语者。傍看春秋左传。似为该实矣。
十七日
晴。风恶气惨。不能上楼。
左传叔向与子产论刑书。可见学识。其曰民知有辟。则不忘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盖任法而不任人。其弊如此。自秦汉以来。大抵任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41H 页
 法。惟孔明用法。得法外意。斯孔明胜子产处。苟有忠信之长。慈惠之师。议事以制。则不必豫设法也。
法。惟孔明用法。得法外意。斯孔明胜子产处。苟有忠信之长。慈惠之师。议事以制。则不必豫设法也。伯宗司马侯言议颇中窾。
子产之不毁游氏庙及司墓之室。不惟惠于国人。亦不为诸侯久留而匆匆行事。亦可见其刚柔并行。子大叔则作事多苟。徒善之人。大抵如此。
毁则朝而塴。不毁则日中而塴。可知随时下棺。未尝择时刻。如后世为也。
华定之来聘。赋蓼萧不知。又不答赋。昭子知其必亡。孔子所谓使四方。不辱君命。必诵诗三百而后。可以如此。若华向者始不习诗。则固陋已矣。何可以必亡判之乎。
朱子曰。古人无受拜礼。虽兄亦答拜。君亦然。受拜者坐受他拜。自己不动也。兄于平日。有答拜之道。则弟死后入庙或上墓。拜之亦可。今人恝然不伸情。于弟之祠墓。盖以拜见为难也。
经典中事实文义。互相牴牾者何限。独有两款事大段可疑。而古来释经者。略不道破。令人腹闷。舜生三十登庸。四岳之荐。帝尧之举。只以其烝烝乂不格奸。而及尧之使九男备百官而事之于畎亩。则
三渊集卷之三十三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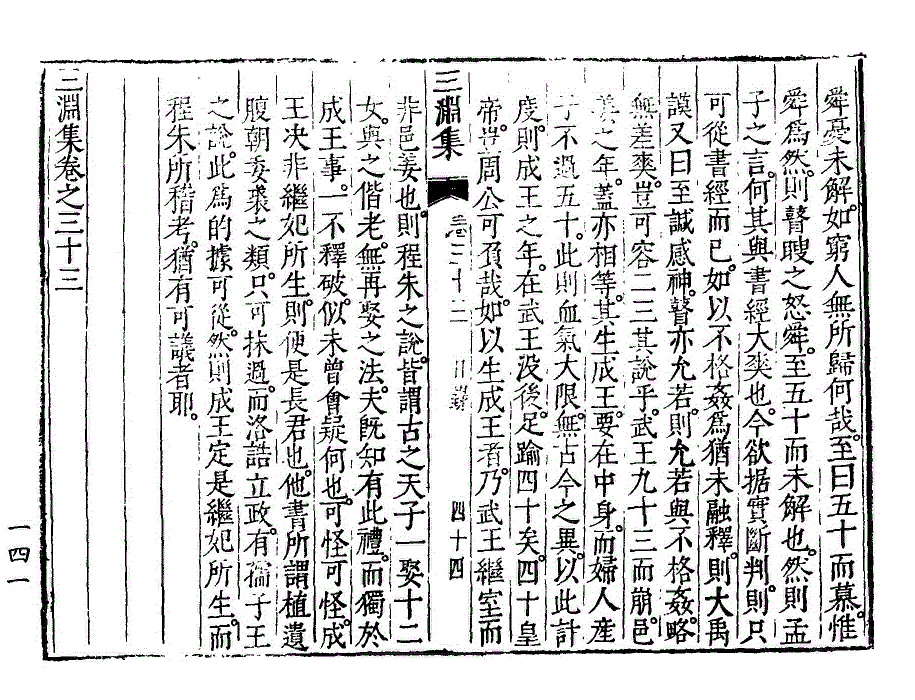 舜忧未解。如穷人无所归何哉。至曰五十而慕。惟舜为然。则瞽瞍之怒舜。至五十而未解也。然则孟子之言。何其与书经大爽也。今欲据实断判。则只可从书经而已。如以不格奸为犹未融释。则大禹谟又曰至諴感神。瞽亦允若。则允若与不格奸。略无差爽。岂可容二三其说乎。武王九十三而崩。邑姜之年。盖亦相等。其生成王。要在中身。而妇人产子不过五十。此则血气大限。无古今之异。以此计度。则成王之年。在武王没后。足踰四十矣。四十皇帝。岂周公可负哉。如以生成王者。乃武王继室而非邑姜也。则程朱之说。皆谓古之天子一娶十二女。与之偕老。无再娶之法。夫既知有此礼。而独于成王事。一不释破。似未曾会疑何也。可怪可怪。成王决非继妃所生。则便是长君也。他书所谓植遗腹朝委裘之类。只可抹过。而洛诰立政。有孺子王之说。此为的据可从。然则成王定是继妃所生。而程朱所稽考。犹有可议者耶。
舜忧未解。如穷人无所归何哉。至曰五十而慕。惟舜为然。则瞽瞍之怒舜。至五十而未解也。然则孟子之言。何其与书经大爽也。今欲据实断判。则只可从书经而已。如以不格奸为犹未融释。则大禹谟又曰至諴感神。瞽亦允若。则允若与不格奸。略无差爽。岂可容二三其说乎。武王九十三而崩。邑姜之年。盖亦相等。其生成王。要在中身。而妇人产子不过五十。此则血气大限。无古今之异。以此计度。则成王之年。在武王没后。足踰四十矣。四十皇帝。岂周公可负哉。如以生成王者。乃武王继室而非邑姜也。则程朱之说。皆谓古之天子一娶十二女。与之偕老。无再娶之法。夫既知有此礼。而独于成王事。一不释破。似未曾会疑何也。可怪可怪。成王决非继妃所生。则便是长君也。他书所谓植遗腹朝委裘之类。只可抹过。而洛诰立政。有孺子王之说。此为的据可从。然则成王定是继妃所生。而程朱所稽考。犹有可议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