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x 页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劄记○中庸
劄记○中庸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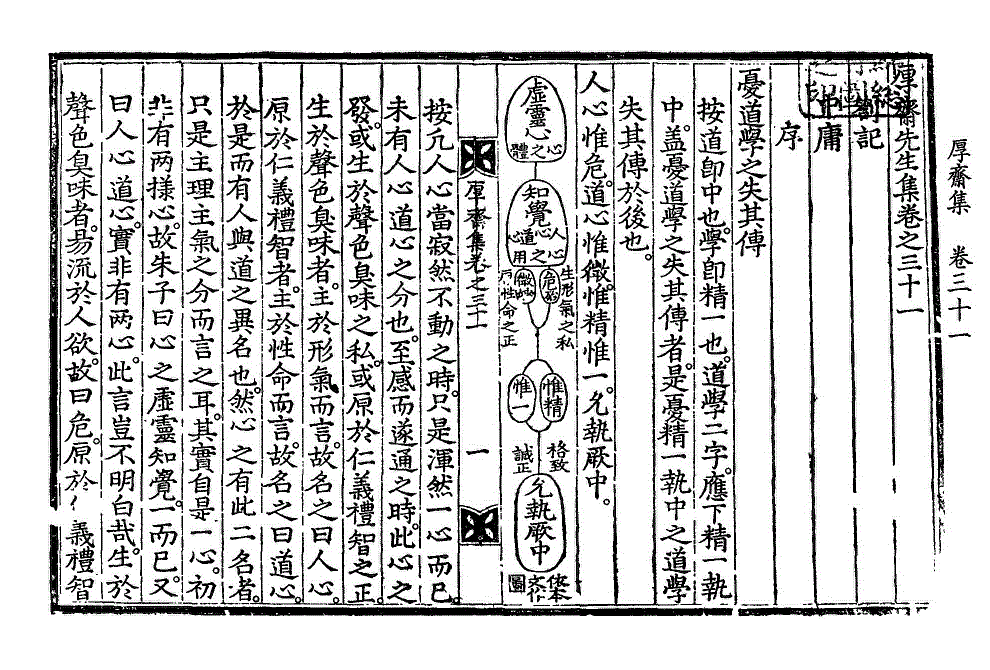 序
序忧道学之失其传
按道即中也。学即精一也。道学二字。应下精一执中。盖忧道学之失其传者。是忧精一执中之道学失其传于后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中庸序
삽화 새창열기
按凡人心当寂然不动之时。只是浑然一心而已。未有人心道心之分也。至感而遂通之时。此心之发。或生于声色臭味之私。或原于仁义礼智之正。生于声色臭味者。主于形气而言。故名之曰人心。原于仁义礼智者。主于性命而言。故名之曰道心。于是而有人与道之异名也。然心之有此二名者。只是主理主气之分而言之耳。其实自是一心。初非有两样心。故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又曰人心道心。实非有两心。此言岂不明白哉。生于声色臭味者。易流于人欲。故曰危。原于仁义礼智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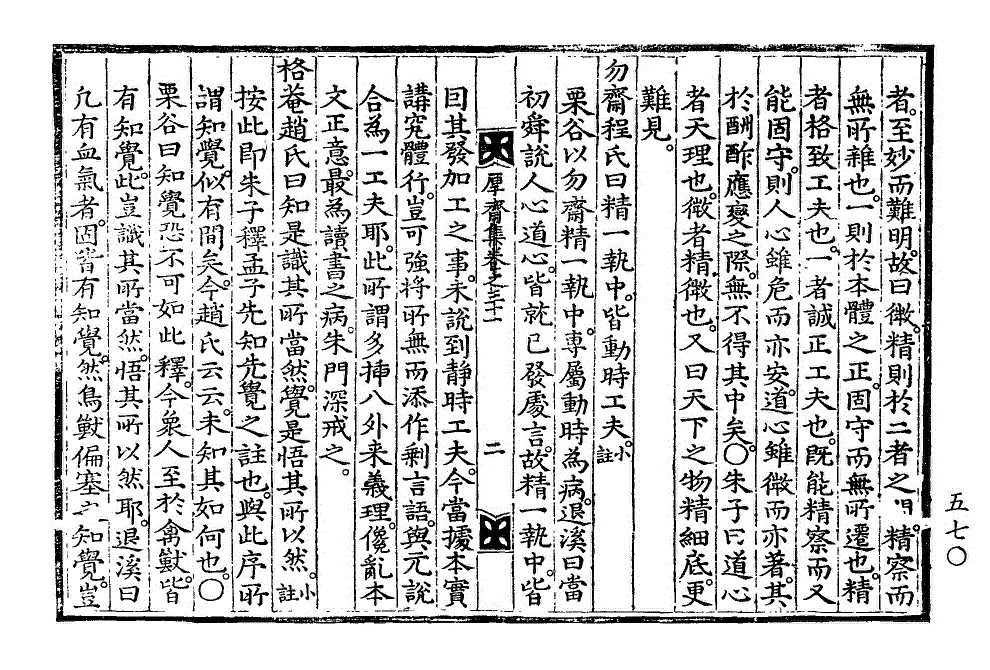 者。至妙而难明。故曰微。精则于二者之间。精察而无所杂也。一则于本体之正。固守而无所迁也。精者格致工夫也。一者诚正工夫也。既能精察而又能固守。则人心虽危而亦安。道心虽微而亦著。其于酬酢应变之际。无不得其中矣。○朱子曰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又曰天下之物精细底。更难见。
者。至妙而难明。故曰微。精则于二者之间。精察而无所杂也。一则于本体之正。固守而无所迁也。精者格致工夫也。一者诚正工夫也。既能精察而又能固守。则人心虽危而亦安。道心虽微而亦著。其于酬酢应变之际。无不得其中矣。○朱子曰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又曰天下之物精细底。更难见。勿斋程氏曰精一执中。皆动时工夫。(小注)
栗谷以勿斋精一执中。专属动时为病。退溪曰当初舜说人心道心。皆就已发处言。故精一执中。皆因其发加工之事。未说到静时工夫。今当据本实讲究体行。岂可强将所无而添作剩言语。与元说合为一工夫耶。此所谓多插八外来义理。儳乱本文正意。最为读书之病。朱门深戒之。
格庵赵氏曰知是识其所当然。觉是悟其所以然。(小注)
按此即朱子释孟子先知先觉之注也。与此序所谓知觉。似有间矣。今赵氏云云。未知其如何也。○栗谷曰知觉恐不可如此释。今众人至于禽兽。皆有知觉。此岂识其所当然。悟其所以然耶。退溪曰凡有血气者。固皆有知觉。然鸟兽偏塞之知觉。岂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1H 页
 同于吾人最灵之知觉乎。况此说知觉。实因传心之法。危微精一之义。而以此二字并虚灵言之。发明人心体用之妙。读者当就吾心知觉处。玩味体认。出正意思来。方见得真实无差。岂可远引鸟兽之知觉。以汨乱正意。而置疑于不当疑之地耶。若夫众人知觉。所以异于圣贤者。乃气拘欲昏而自失之。又岂当缘此而疑人心之不能识与悟耶。沙溪曰知其所当然。觉其所以然。本出孟子注。盖孟子所引伊尹之言。既以知与觉分而言之。此固有浅深之异矣。若此谓知觉则只是不昏塞之意。故朱子尝以知寒觉煖为训。赵说恐非序文本意。
同于吾人最灵之知觉乎。况此说知觉。实因传心之法。危微精一之义。而以此二字并虚灵言之。发明人心体用之妙。读者当就吾心知觉处。玩味体认。出正意思来。方见得真实无差。岂可远引鸟兽之知觉。以汨乱正意。而置疑于不当疑之地耶。若夫众人知觉。所以异于圣贤者。乃气拘欲昏而自失之。又岂当缘此而疑人心之不能识与悟耶。沙溪曰知其所当然。觉其所以然。本出孟子注。盖孟子所引伊尹之言。既以知与觉分而言之。此固有浅深之异矣。若此谓知觉则只是不昏塞之意。故朱子尝以知寒觉煖为训。赵说恐非序文本意。生于形气之私。原于性命之正。
按生是从中生出之意。所谓生于形气者。言人心自耳目口鼻之私而生也。原是沿流溯源之意。所谓原于性命者。言道心根于仁义礼智之性也。
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云云。(小注)
按本文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朱子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曰云云。始知靠不得以上十一字。乃朱子说也。
云峰胡氏曰生是气用事时方生。(小注)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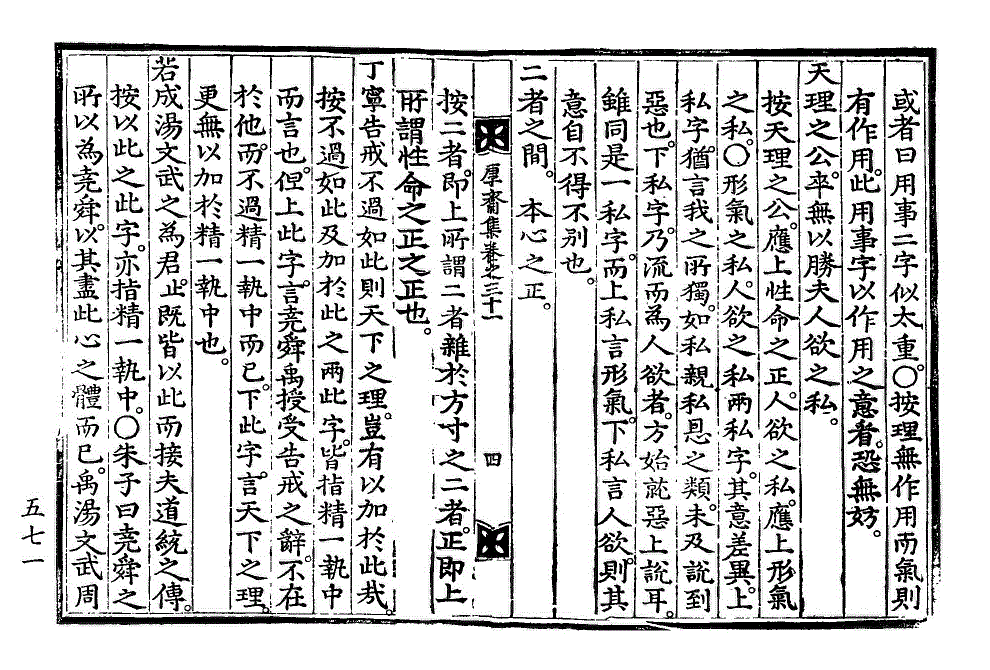 或者曰用事二字似太重。○按理无作用而气则有作用。此用事字以作用之意看。恐无妨。
或者曰用事二字似太重。○按理无作用而气则有作用。此用事字以作用之意看。恐无妨。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
按天理之公。应上性命之正。人欲之私。应上形气之私。○形气之私。人欲之私两私字。其意差异。上私字。犹言我之所独。如私亲私恩之类。未及说到恶也。下私字。乃流而为人欲者。方始就恶上说耳。虽同是一私字。而上私言形气。下私言人欲。则其意自不得不别也。
二者之间。 本心之正。
按二者。即上所谓二者杂于方寸之二者。正即上所谓性命之正之正也。
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按不过如此及加于此之两此字。皆指精一执中而言也。但上此字。言尧舜禹授受告戒之辞。不在于他。而不过精一执中而已。下此字。言天下之理。更无以加于精一执中也。
若成汤文武之为君。止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
按以此之此字。亦指精一执中。○朱子曰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禹汤文武周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2H 页
 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者则为得其传耳。○蔡氏清曰独举皋陶而不及益,稷,契。盖亦举其尤者。故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则固已不及益,稷,契矣。
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者则为得其传耳。○蔡氏清曰独举皋陶而不及益,稷,契。盖亦举其尤者。故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则固已不及益,稷,契矣。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
蔡氏清曰先儒谓颜子博文精也。约礼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诚正一也。其说固善。但于颜,曾之所以独得其宗者。似有未尽。盖博文约礼。格致诚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设教。而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七十子亦尝用其力者。要必言颜氏由博约之诲而至于见所立之卓尔。曾子极格致诚正之功而至于唯。吾道之一贯。方见颜,曾之独得其宗。而非他人所得与处。
历选
历。遍数也。选犹考也。
异端之说。日新月盛。
蔡氏清曰承上文孟子没而遂失其传。是指孟子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2L 页
 没后之异端也。许氏兼杨,墨言恐非是。杨,墨在孟子时已辟之矣。不复昌炽于后。惟若荀,杨性恶善恶混之说。庄生,列御寇虚诞之说。申不害,韩非刑名之说。鬼谷,孙吴权谋之说。秦汉间迂怪之士。神仙黄白之说。凡一切惑世诬民。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皆是也。
没后之异端也。许氏兼杨,墨言恐非是。杨,墨在孟子时已辟之矣。不复昌炽于后。惟若荀,杨性恶善恶混之说。庄生,列御寇虚诞之说。申不害,韩非刑名之说。鬼谷,孙吴权谋之说。秦汉间迂怪之士。神仙黄白之说。凡一切惑世诬民。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皆是也。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按老佛之学。以清净寡欲。为治心工夫。而以空虚寂灭为性。夫以清净寡欲治心则似乎近理。而以空虚寂灭为性则便截然相悖。所以大乱真矣。曰弥近理者。言老佛之道。于理相去不远。下一近字。可见其甚相似也。曰大乱真者。言彼之伪道。便能大乱此之真道。于此直下大乱二字。可见其绝不同也。然以其甚相似。故能大乱真也。
石氏之所辑录
按石氏名塾。字子重。号克斋。台州临海人。
子思之功。于是为大。
蔡氏清曰惟程子得有所考。以续千载不传之绪。则子思忧失其传者。今得其传矣。得其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则子思惧失其真者。今不失其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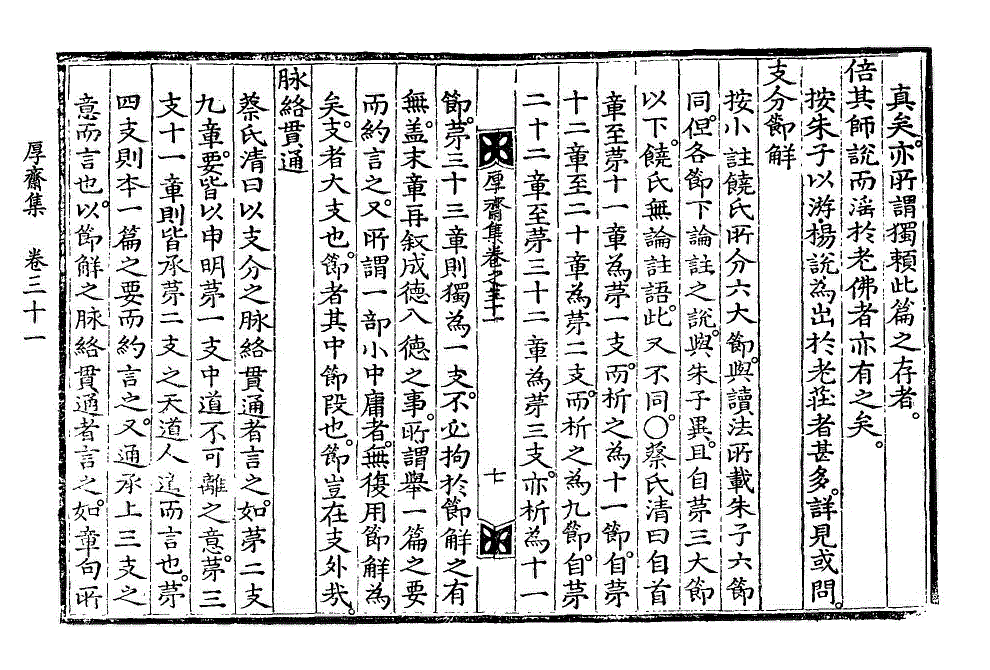 真矣。亦所谓独赖此篇之存者。
真矣。亦所谓独赖此篇之存者。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按朱子以游,杨说为出于老庄者甚多。详见或问。
支分节解
按小注饶氏所分六大节。与读法所载朱子六节同。但各节下论注之说。与朱子异。且自第三大节以下。饶氏无论注语。此又不同。○蔡氏清曰自首章至第十一章为第一支。而析之为十一节。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为第二支。而析之为九节。自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为第三支。亦析为十一节。第三十三章则独为一支。不必拘于节解之有无。盖末章再叙成德入德之事。所谓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又所谓一部小中庸者。无复用节解为矣。支者大支也。节者其中节段也。节岂在支外哉。
脉络贯通
蔡氏清曰以支分之脉络贯通者言之。如第二支九章。要皆以申明第一支中道不可离之意。第三支十一章则皆承第二支之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则本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又通承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节解之脉络贯通者言之。如章句所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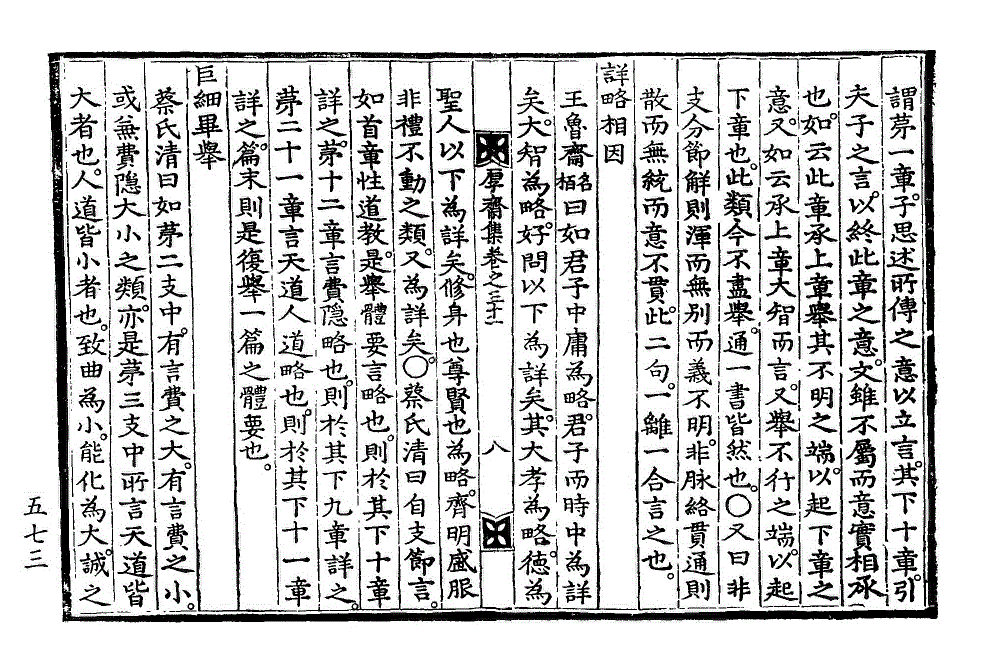 谓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意。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举其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智而言。又举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也。此类今不尽举。通一书皆然也。○又曰非支分节解则浑而无别而义不明。非脉络贯通则散而无统而意不贯。此二句。一离一合言之也。
谓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意。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举其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智而言。又举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也。此类今不尽举。通一书皆然也。○又曰非支分节解则浑而无别而义不明。非脉络贯通则散而无统而意不贯。此二句。一离一合言之也。详略相因
王鲁斋(名柏)曰如君子中庸为略。君子而时中为详矣。大智为略。好问以下为详矣。其大孝为略。德为圣人以下为详矣。修身也尊贤也为略。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之类。又为详矣。○蔡氏清曰自支节言。如首章性道教。是举体要言略也。则于其下十章详之。第十二章言费隐略也。则于其下九章详之。第二十一章言天道人道略也。则于其下十一章详之。篇末则是复举一篇之体要也。
巨细毕举
蔡氏清曰如第二支中。有言费之大。有言费之小。或兼费隐大小之类。亦是第三支中所言天道皆大者也。人道皆小者也。致曲为小。能化为大。诚之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4H 页
 为小。时措之宜为大。又如尊德性以极道体之大者为大。道问学以尽道体之细者为小。故章句大小相资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内外该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细。但不可拘于此耳。末章则自下学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其极。巨细毕举又明矣。
为小。时措之宜为大。又如尊德性以极道体之大者为大。道问学以尽道体之细者为小。故章句大小相资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内外该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细。但不可拘于此耳。末章则自下学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其极。巨细毕举又明矣。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按不偏不倚。以在心之中言。盖未发之时。不偏于喜不偏于怒。只是浑然本体在中而已。故于此下不偏不倚字。无过不及。以在事物之中言。盖既发之后在事在物。各当其理。既无所过。又无不及。只合于十分恰好处。故于此下无过不及字。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皆是释中字。而然细究主意所在。自不无分别也。
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为怪异之事。(止)夷齐所为。都不是庸了。(小注)
朱子曰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其变无穷。亦无适而非平常。○按尧舜之事。汤武之举。夷齐之为。皆是处变而得中者。既是得中。则同谓之平常可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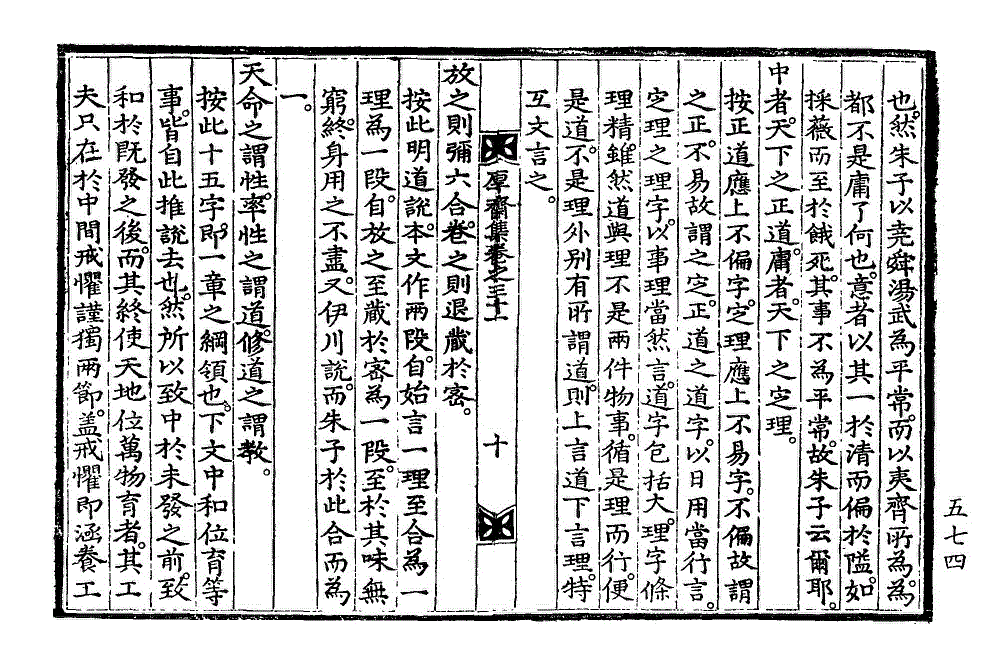 也。然朱子以尧舜汤武为平常。而以夷齐所为。为都不是庸了何也。意者以其一于清而偏于隘。如采薇而至于饿死。其事不为平常。故朱子云尔耶。
也。然朱子以尧舜汤武为平常。而以夷齐所为。为都不是庸了何也。意者以其一于清而偏于隘。如采薇而至于饿死。其事不为平常。故朱子云尔耶。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按正道应上不偏字。定理应上不易字。不偏故谓之正。不易故谓之定。正道之道字。以日用当行言。定理之理字。以事理当然言。道字包括大。理字条理精。虽然道与理不是两件物事。循是理而行。便是道。不是理外别有所谓道。则上言道下言理。特互文言之。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按此明道说。本文作两段。自始言一理至合为一理为一段。自放之至藏于密为一段。至于其味无穷。终身用之不尽。又伊川说。而朱子于此合而为一。
[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按此十五字。即一章之纲领也。下文中和位育等事。皆自此推说去也。然所以致中于未发之前。致和于既发之后。而其终使天地位万物育者。其工夫只在于中间。戒惧谨独两节。盖戒惧即涵养工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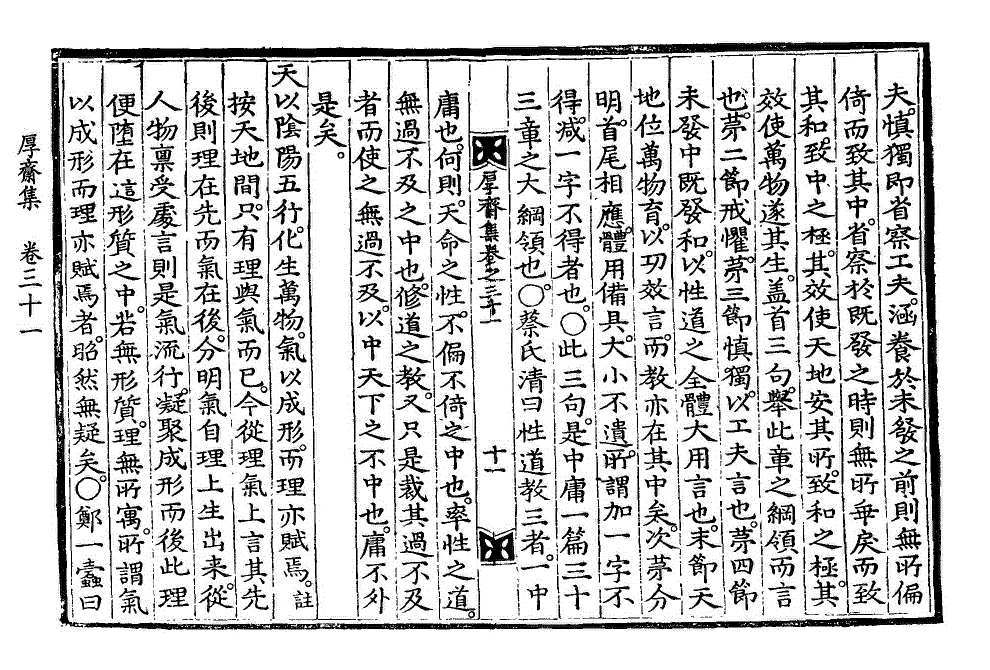 夫。慎独即省察工夫。涵养于未发之前则无所偏倚而致其中。省察于既发之时则无所乖戾而致其和。致中之极。其效使天地安其所。致和之极。其效使万物遂其生。盖首三句。举此章之纲领而言也。第二节戒惧。第三节慎独。以工夫言也。第四节未发中既发和。以性道之全体大用言也。末节天地位万物育。以功效言。而教亦在其中矣。次第分明。首尾相应。体用备具。大小不遗。所谓加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者也。○此三句。是中庸一篇三十三章之大纲领也。○蔡氏清曰性道教三者。一中庸也。何则。天命之性。不偏不倚之中也。率性之道。无过不及之中也。修道之教。又只是裁其过不及者而使之无过不及。以中天下之不中也。庸不外是矣。
夫。慎独即省察工夫。涵养于未发之前则无所偏倚而致其中。省察于既发之时则无所乖戾而致其和。致中之极。其效使天地安其所。致和之极。其效使万物遂其生。盖首三句。举此章之纲领而言也。第二节戒惧。第三节慎独。以工夫言也。第四节未发中既发和。以性道之全体大用言也。末节天地位万物育。以功效言。而教亦在其中矣。次第分明。首尾相应。体用备具。大小不遗。所谓加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者也。○此三句。是中庸一篇三十三章之大纲领也。○蔡氏清曰性道教三者。一中庸也。何则。天命之性。不偏不倚之中也。率性之道。无过不及之中也。修道之教。又只是裁其过不及者而使之无过不及。以中天下之不中也。庸不外是矣。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注)
按天地间。只有理与气而已。今从理气上言其先后则理在先而气在后。分明气自理上生出来。从人物禀受处言则是气流行。凝聚成形而后此理便堕在这形质之中。若无形质。理无所寓。所谓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昭然无疑矣。○郑一蠹曰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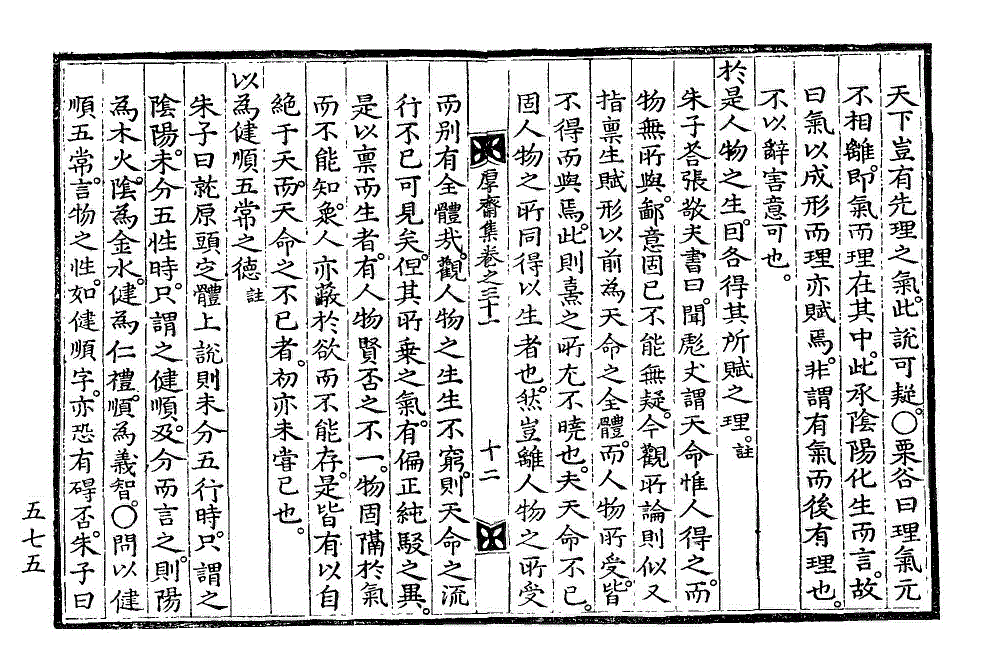 天下岂有先理之气。此说可疑。○栗谷曰理气元不相离。即气而理在其中。此承阴阳化生而言。故曰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非谓有气而后有理也。不以辞害意可也。
天下岂有先理之气。此说可疑。○栗谷曰理气元不相离。即气而理在其中。此承阴阳化生而言。故曰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非谓有气而后有理也。不以辞害意可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注)
朱子答张敬夫书曰。闻彪丈谓天命惟人得之。而物无所与。鄙意固已不能无疑。今观所论则似又指禀生赋形以前为天命之全体。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与焉。此则熹之所尤不晓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岂离人物之所受而别有全体哉。观人物之生生不穷。则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见矣。但其所乘之气。有偏正纯驳之异。是以禀而生者。有人物贤否之不一。物固隔于气而不能知。众人亦蔽于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绝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尝已也。
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注)
朱子曰就原头定体上说则未分五行时。只谓之阴阳。未分五性时。只谓之健顺。及分而言之。则阳为木火。阴为金水。健为仁礼。顺为义智。○问以健顺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顺字。亦恐有碍否。朱子曰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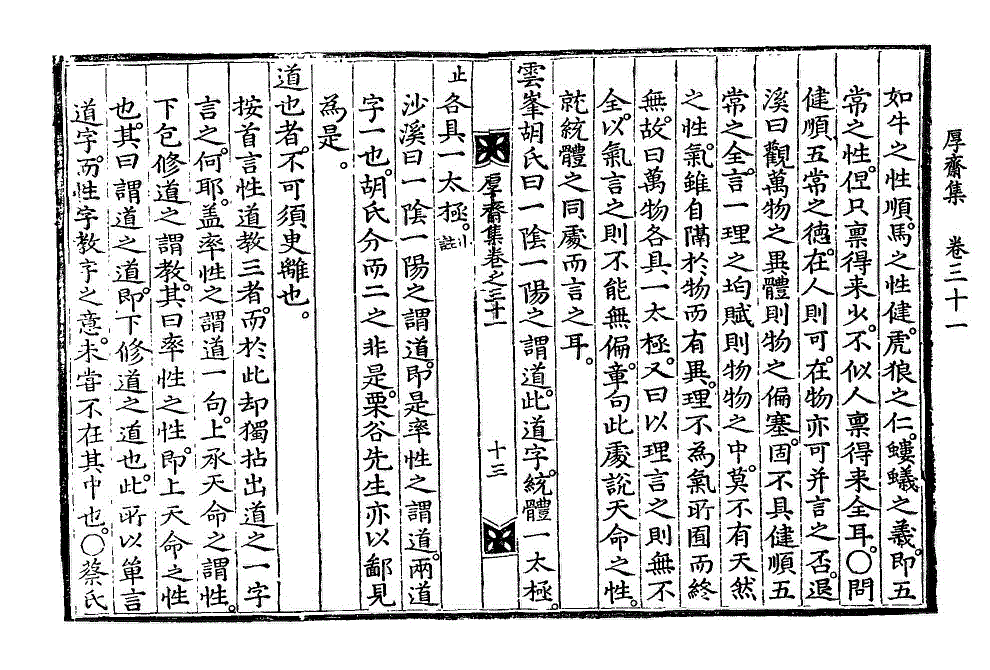 如牛之性顺。马之性健。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只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问健顺五常之德。在人则可。在物亦可并言之否。退溪曰观万物之异体则物之偏塞。固不具健顺五常之全。言一理之均赋则物物之中。莫不有天然之性。气虽自隔于物而有异。理不为气所囿而终无。故曰万物各具一太极。又曰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章句此处说天命之性。就统体之同处而言之耳。
如牛之性顺。马之性健。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只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问健顺五常之德。在人则可。在物亦可并言之否。退溪曰观万物之异体则物之偏塞。固不具健顺五常之全。言一理之均赋则物物之中。莫不有天然之性。气虽自隔于物而有异。理不为气所囿而终无。故曰万物各具一太极。又曰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章句此处说天命之性。就统体之同处而言之耳。云峰胡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字。统体一太极。(止)各具一太极。(小注)
沙溪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率性之谓道。两道字一也。胡氏分而二之非是。栗谷先生亦以鄙见为是。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按首言性道教三者。而于此却独拈出道之一字言之。何耶。盖率性之谓道一句。上承天命之谓性。下包修道之谓教。其曰率性之性。即上天命之性也。其曰谓道之道。即下修道之道也。此所以单言道字。而性字教字之意。未尝不在其中也。○蔡氏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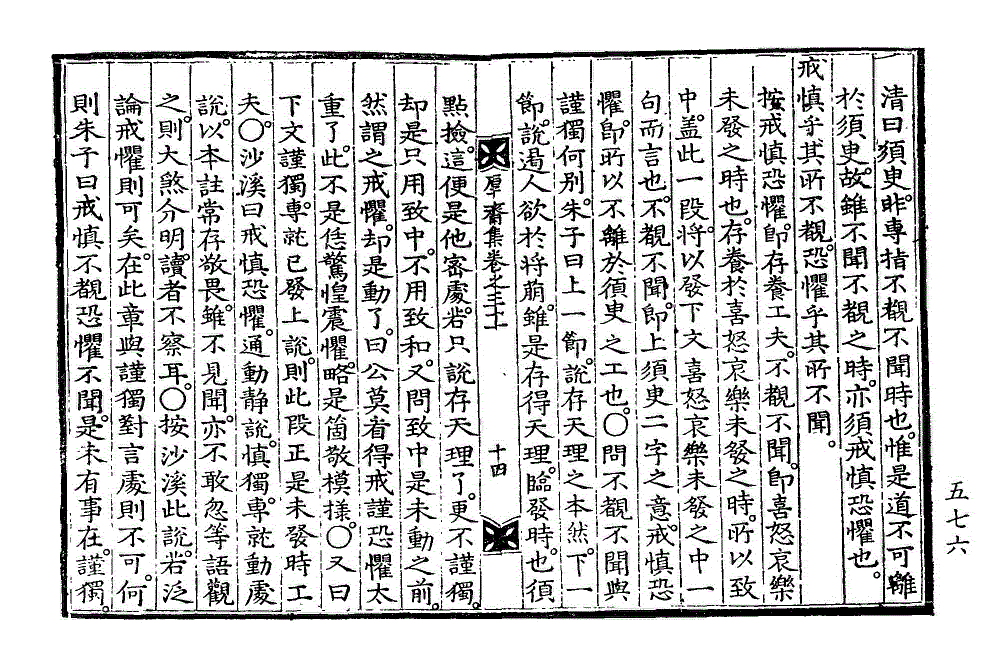 清曰须臾。非专指不睹不闻时也。惟是道不可离于须臾。故虽不闻不睹之时。亦须戒慎恐惧也。
清曰须臾。非专指不睹不闻时也。惟是道不可离于须臾。故虽不闻不睹之时。亦须戒慎恐惧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按戒慎恐惧。即存养工夫。不睹不闻。即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所以致中。盖此一段。将以发下文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句而言也。不睹不闻。即上须臾二字之意。戒慎恐惧。即所以不离于须臾之工也。○问不睹不闻与谨独何别。朱子曰上一节。说存天理之本然。下一节。说遏人欲于将萌。虽是存得天理。临发时。也须点检。这便是他密处。若只说存天理了。更不谨独。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又问致中是未动之前。然谓之戒惧。却是动了。曰公莫看得戒谨恐惧太重了。此不是恁惊惶震惧。略是个敬模样。○又曰下文谨独。专就已发上说。则此段正是未发时工夫。○沙溪曰戒慎恐惧。通动静说。慎独。专就动处说。以本注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等语观之。则大煞分明。读者不察耳。○按沙溪此说。若泛论戒惧则可矣。在此章与谨独对言处则不可。何则朱子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未有事在。谨独。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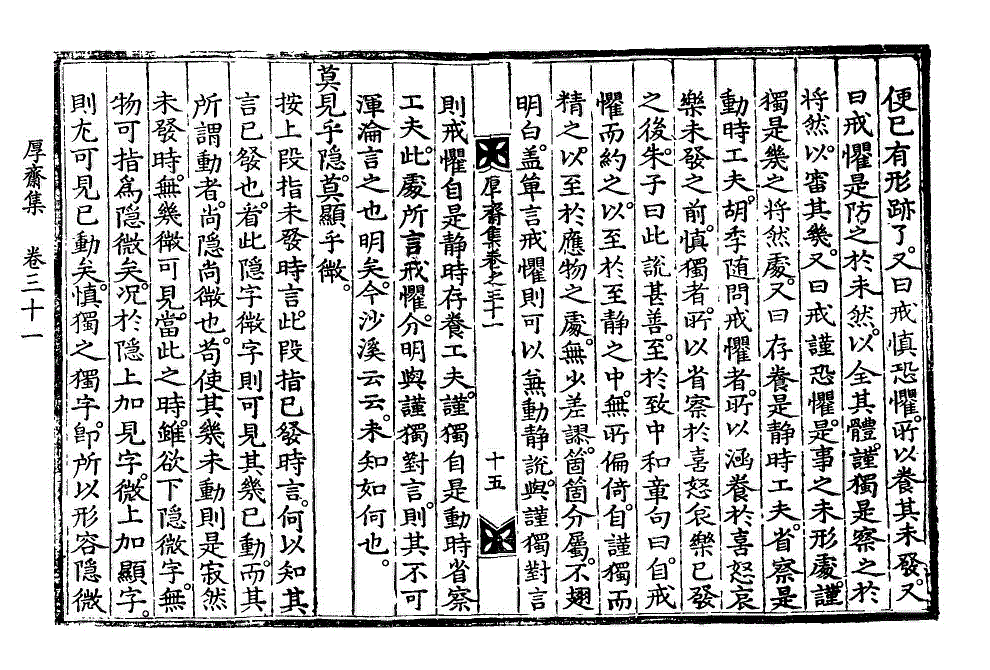 便已有形迹了。又曰戒慎恐惧。所以养其未发。又曰戒惧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几。又曰戒谨恐惧。是事之未形处。谨独是几之将然处。又曰存养是静时工夫。省察是动时工夫。胡季随问戒惧者。所以涵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慎独者。所以省察于喜怒哀乐已发之后。朱子曰此说甚善。至于致中和章句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个个分属。不翅明白。盖单言戒惧则可以兼动静说。与谨独对言则戒惧自是静时存养工夫。谨独自是动时省察工夫。此处所言戒惧。分明与谨独对言。则其不可浑沦言之也明矣。今沙溪云云。未知如何也。
便已有形迹了。又曰戒慎恐惧。所以养其未发。又曰戒惧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几。又曰戒谨恐惧。是事之未形处。谨独是几之将然处。又曰存养是静时工夫。省察是动时工夫。胡季随问戒惧者。所以涵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慎独者。所以省察于喜怒哀乐已发之后。朱子曰此说甚善。至于致中和章句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个个分属。不翅明白。盖单言戒惧则可以兼动静说。与谨独对言则戒惧自是静时存养工夫。谨独自是动时省察工夫。此处所言戒惧。分明与谨独对言。则其不可浑沦言之也明矣。今沙溪云云。未知如何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按上段指未发时言。此段指已发时言。何以知其言已发也。看此隐字微字则可见其几已动。而其所谓动者。尚隐尚微也。苟使其几未动则是寂然未发时。无几微可见。当此之时。虽欲下隐微字。无物可指为隐微矣。况于隐上加见字。微上加显字。则尤可见已动矣。慎独之独字。即所以形容隐微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7L 页
 字。非隐微外复别有所谓独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处。则正是指几动隐微处而言也。
字。非隐微外复别有所谓独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处。则正是指几动隐微处而言也。君子慎其独也。
按慎即省察工夫。独即喜怒哀乐将发之际也。省察于喜怒哀乐将发之际。所以致和。盖此一段。将以发下文发而皆中节之和一句而言也。○独者是一念才起处则是已动而但隐微未见显耳。善恶之分。正在此处。今于一念才起隐微处必慎之。则可以见不可须臾离之意也。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注)
问上两句。是程子意。下两句是游氏意。先生则合而论之是否。朱子曰然。两事只是一理。气既动而己必知之。己既知之则人必知之。
双峰饶氏曰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见得下面。(止)见与显皆是此道。(小注)
栗谷曰幽暗之中细微之事。有邪有正。乌可谓之皆是道耶。退溪曰观朱子及诸说。皆以善恶之几言。饶说果为未安。盖子思朱子意本谓道无不在。而隐微之见显不可掩也。故慎其独。所以存其道云尔。非谓见显是道也。○沙溪曰或云朱子曰莫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8H 页
 见乎隐莫显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饶说更当商量。
见乎隐莫显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饶说更当商量。双峰饶氏曰大学只言慎独。不言戒惧。初学之士。且令于动处做工夫。(小注)
按中庸首章兼言戒惧慎独。盖是章言未发之中已发之和。而戒惧是未发前存养工夫也。慎独是已发时省察工夫也。故并举而全言之也。大学诚意章单言慎独。盖是章言诚意事。意是一念初萌处也。一念初萌。是已发时也。只言已发而不言未发。故只举省察工夫而单言之也。今饶氏云云。未知如何也。○退溪答栗谷曰大学固不言戒惧矣。故朱子于正心章注。亦只举察字以直解本文正意。惟于视听注。始拈出存字敬字而言之。亦因传者说无心之病。故以此救其病。而戒惧之功。隐然在不言中矣。云峰胡氏前念后事之说。意亦如此。皆未尝云正心章说戒惧也。今来喻直以正心章当戒惧。非也。来喻又云无戒惧之功。何以明明德。此则然矣。故朱子说古人涵养本源。小学已至。大学直以格致为先云。又患后世之不能然则以敬字补小学之阙功。今亦只当依此而用功。又当知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8L 页
 大学虽不言戒惧。而有曰顾諟曰敬止。则其中自兼戒惧之意。有曰定曰静。虽是知止之效。而静时工夫亦不外是。如是为言则可矣。何可以所不言。而强以为已言耶。
大学虽不言戒惧。而有曰顾諟曰敬止。则其中自兼戒惧之意。有曰定曰静。虽是知止之效。而静时工夫亦不外是。如是为言则可矣。何可以所不言。而强以为已言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按未发之中。是大本。则即所谓天命之性。道心之所原也。既发之和。是达道。则即所谓率性之道。人心之合理。而道心之流行者也。○未发之中。即性之德也。发而皆中节。即情之正也。心者所以统未发之性已发之情。故心之体谓之性。心之用谓之情。则上所谓戒惧。所以存养此心之体也。上所谓慎独。所以省察此心之用也。此心体用之外。非别有所谓未发中已发和。则此章上下。虽不言心字。然实未尝离心而言者。可知也。○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即不偏不倚之中也。发而皆中节之和。即无过不及之中也。○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或曰恐众人未发。与圣人异否。曰未发只做得未发。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或曰恐众人于未发昏了否。曰这里未有昏明。须是还他做未发。若论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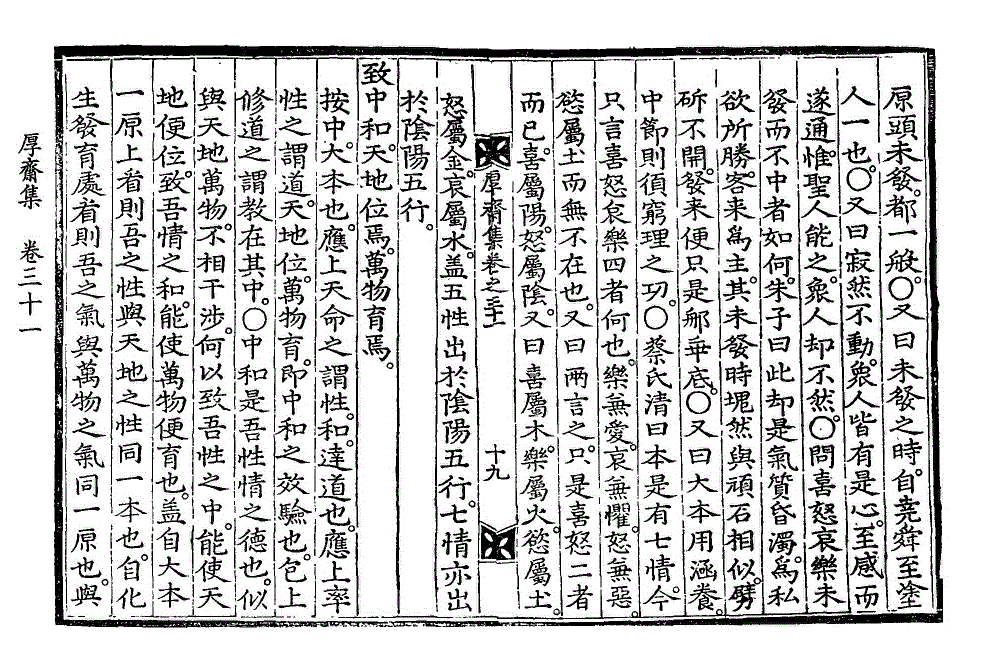 原头未发。都一般。○又曰未发之时。自尧舜至涂人一也。○又曰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圣人能之。众人却不然。○问喜怒哀乐未发而不中者如何。朱子曰此却是气质昏浊。为私欲所胜。客来为主。其未发时块然与顽石相似。劈斫不开。发来便只是那乖底。○又曰大本用涵养。中节则须穷理之功。○蔡氏清曰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乐四者何也。乐兼爱。哀兼惧。怒兼恶。欲属土而无不在也。又曰两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属阳。怒属阴。又曰喜属木。乐属火。欲属土。怒属金。哀属水。盖五性出于阴阳五行。七情亦出于阴阳五行。
原头未发。都一般。○又曰未发之时。自尧舜至涂人一也。○又曰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圣人能之。众人却不然。○问喜怒哀乐未发而不中者如何。朱子曰此却是气质昏浊。为私欲所胜。客来为主。其未发时块然与顽石相似。劈斫不开。发来便只是那乖底。○又曰大本用涵养。中节则须穷理之功。○蔡氏清曰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乐四者何也。乐兼爱。哀兼惧。怒兼恶。欲属土而无不在也。又曰两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属阳。怒属阴。又曰喜属木。乐属火。欲属土。怒属金。哀属水。盖五性出于阴阳五行。七情亦出于阴阳五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按中。大本也。应上天命之谓性。和。达道也。应上率性之谓道。天地位。万物育。即中和之效验也。包上修道之谓教在其中。○中和是吾性情之德也。似与天地万物。不相干涉。何以致吾性之中。能使天地便位。致吾情之和。能使万物便育也。盖自大本一原上看则吾之性与天地之性同一本也。自化生发育处看则吾之气与万物之气同一原也。与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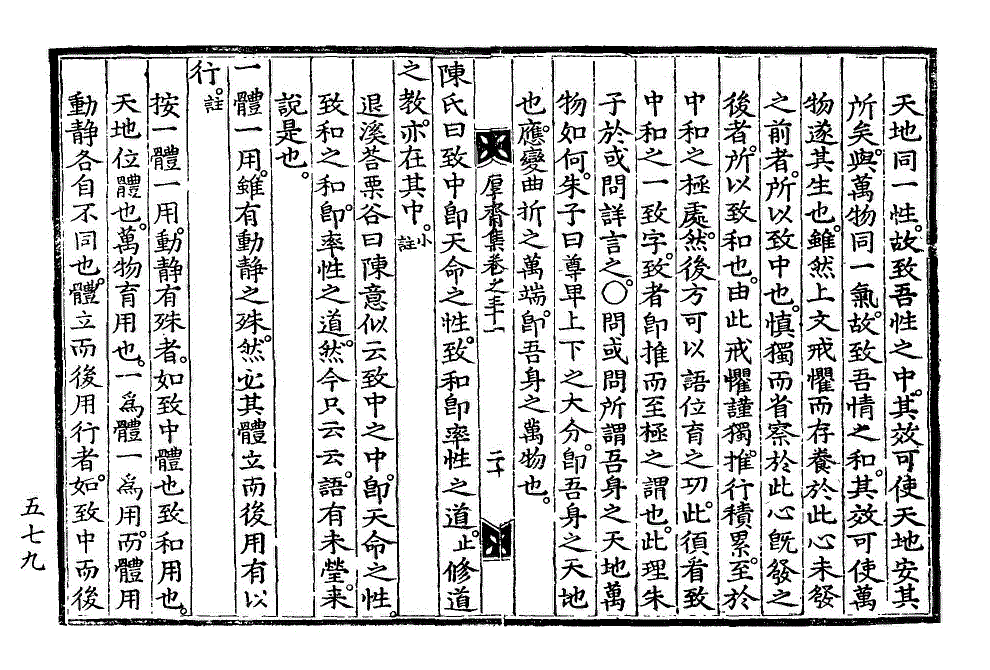 天地同一性。故致吾性之中。其效可使天地安其所矣。与万物同一气。故致吾情之和。其效可使万物遂其生也。虽然上文戒惧而存养于此心未发之前者。所以致中也。慎独而省察于此心既发之后者。所以致和也。由此戒惧谨独。推行积累。至于中和之极处。然后方可以语位育之功。此须看致中和之一致字。致者即推而至极之谓也。此理朱子于或问详言之。○问或问所谓吾身之天地万物如何。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应变曲折之万端。即吾身之万物也。
天地同一性。故致吾性之中。其效可使天地安其所矣。与万物同一气。故致吾情之和。其效可使万物遂其生也。虽然上文戒惧而存养于此心未发之前者。所以致中也。慎独而省察于此心既发之后者。所以致和也。由此戒惧谨独。推行积累。至于中和之极处。然后方可以语位育之功。此须看致中和之一致字。致者即推而至极之谓也。此理朱子于或问详言之。○问或问所谓吾身之天地万物如何。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应变曲折之万端。即吾身之万物也。陈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止)修道之教。亦在其中。(小注)
退溪答栗谷曰陈意似云致中之中。即天命之性。致和之和。即率性之道。然今只云云。语有未莹。来说是也。
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注)
按一体一用。动静有殊者。如致中体也致和用也。天地位体也。万物育用也。一为体一为用。而体用动静各自不同也。体立而后用行者。如致中而后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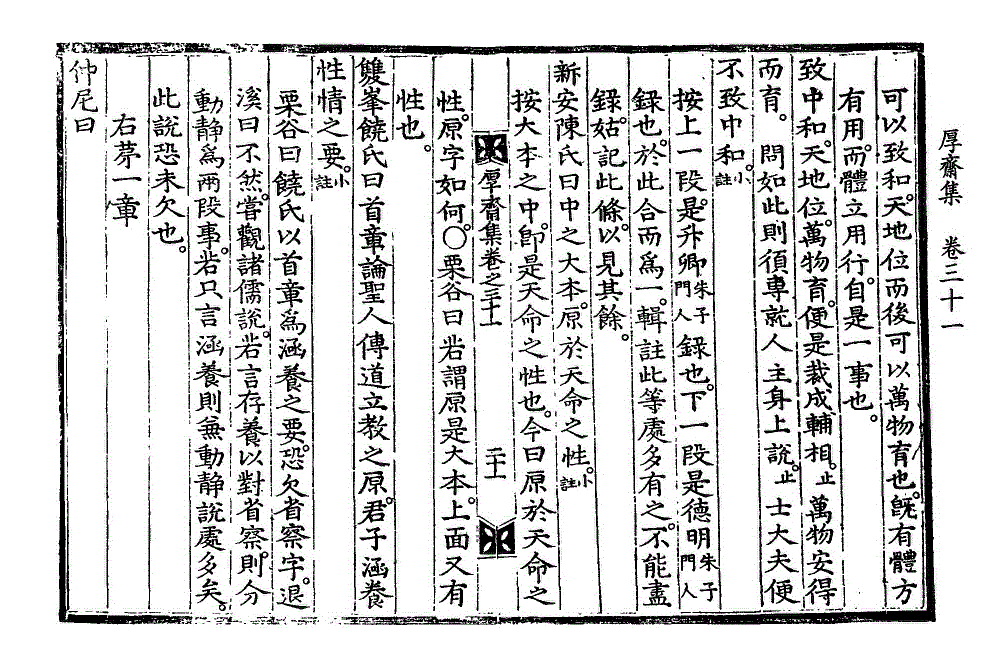 可以致和。天地位而后可以万物育也。既有体方有用。而体立用行。自是一事也。
可以致和。天地位而后可以万物育也。既有体方有用。而体立用行。自是一事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便是裁成辅相。(止)万物安得而育。(止)问如此则须专就人主身上说。(止)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小注)
按上一段。是升卿(朱子门人)录也。下一段是德明(朱子门人)录也。于此合而为一。辑注此等处多有之。不能尽录。姑记此条。以见其馀。
新安陈氏曰中之大本。原于天命之性。(小注)
按大本之中。即是天命之性也。今曰原于天命之性。原字如何。○栗谷曰若谓原是大本。上面又有性也。
双峰饶氏曰首章论圣人传道立教之原。君子涵养性情之要。(小注)
栗谷曰饶氏以首章为涵养之要。恐欠省察字。退溪曰不然。尝观诸儒说。若言存养以对省察。则分动静为两段事。若只言涵养则兼动静说处多矣。此说恐未欠也。
(右第一章)
[第二章]
仲尼曰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0L 页
 问以仲尼曰称之。而下文例以子曰称之者。何义。退溪曰首称仲尼以表之。则其后例称子曰。亦非泛然也。
问以仲尼曰称之。而下文例以子曰称之者。何义。退溪曰首称仲尼以表之。则其后例称子曰。亦非泛然也。精微之极致。惟君子为能体之。(注)
按精微极致。非惟精不能知也。君子能体。非惟一不能体也。
君子之中庸也
问君子之中庸一节。蔡氏以为子思释孔子之言。然否。退溪曰君子之中庸以下。朱子亦以为孔子之言。故不云子思之言。蔡氏特备一说。未必为是。
新安陈氏曰无忌与戒慎反。无惮与恐惧反。(小注)
按陈氏分忌惮为二未知如何也
鲁斋许氏曰君子戒慎恐惧。存于未发之前。察于既发之际。(小注)
按戒惧是存养于未发前工夫也。慎独是省察于既发际工夫也。今许氏只言戒慎恐惧。不言慎独。而乃混沦言之曰存于未发之前。察于既发之际。恐似未备。○金叔涵曰戒慎恐惧。自是兼动静工夫。静而所以存之。不能无赖于此。动而所以察之。亦不能无赖于此。然则存之察之。虽有动静之别。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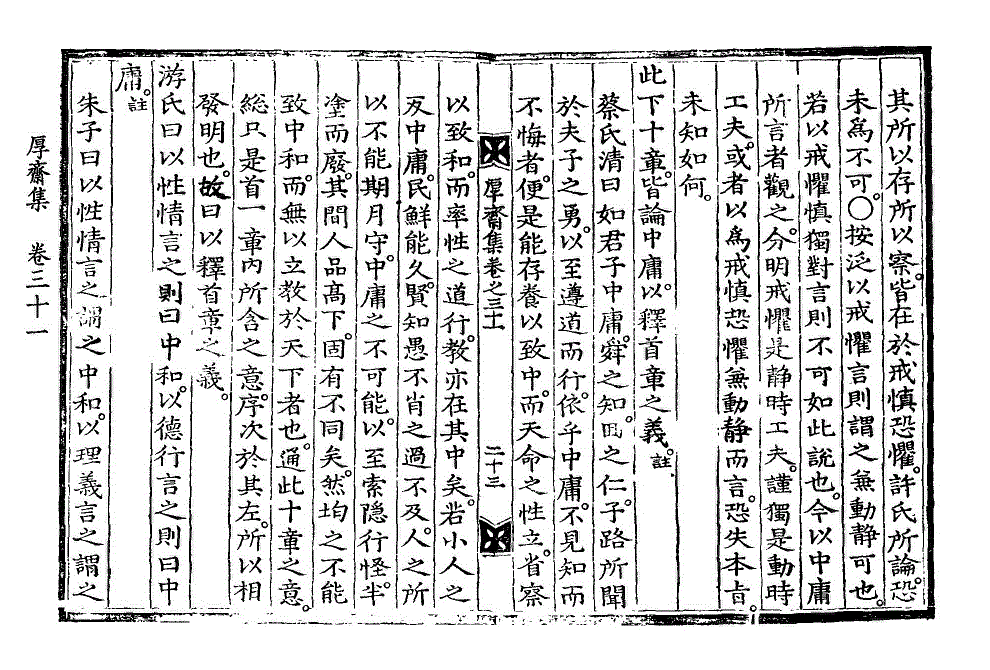 其所以存所以察。皆在于戒慎恐惧。许氏所论。恐未为不可。○按泛以戒惧言则谓之兼动静可也。若以戒惧慎独对言则不可如此说也。今以中庸所言者观之。分明戒惧是静时工夫。谨独是动时工夫。或者以为戒慎恐惧兼动静而言。恐失本旨。未知如何。
其所以存所以察。皆在于戒慎恐惧。许氏所论。恐未为不可。○按泛以戒惧言则谓之兼动静可也。若以戒惧慎独对言则不可如此说也。今以中庸所言者观之。分明戒惧是静时工夫。谨独是动时工夫。或者以为戒慎恐惧兼动静而言。恐失本旨。未知如何。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注)
蔡氏清曰如君子中庸。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闻于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见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养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鲜能久。贤知愚不肖之过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隐行怪。半涂而废。其间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矣。然均之不能致中和。而无以立教于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意。总只是首一章内所含之意。序次于其左。所以相发明也。故曰以释首章之义。
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注)
朱子曰以性情言之谓之中和。以理义言之谓之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1L 页
 中庸。其实一也。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指已发未发而言。以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蔡氏清曰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谓君子之德也。无过不及之中。行也。所谓随时以处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中庸。其实一也。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指已发未发而言。以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蔡氏清曰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谓君子之德也。无过不及之中。行也。所谓随时以处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黄氏曰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小注)
按中者性之德也。和者情之德。而行是德之见于行事者。然则中和在性情为德。而见于事为行也。性情中和之德之外。更无别样所谓德行也。今黄氏之说如此。未知如何也。
双峰饶氏曰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止)内外交相养之道也。(小注)
栗谷曰中和中庸。不可分内外。退溪曰中和中庸。以理言之。固非二事。然以所就而言之地头论之。安得不异。今以游氏说观之。以性情言之曰中和。既曰性情。非内乎。以德行言之曰中庸。既曰德行。以对性情则宁不可谓之外乎。德以行道有得言。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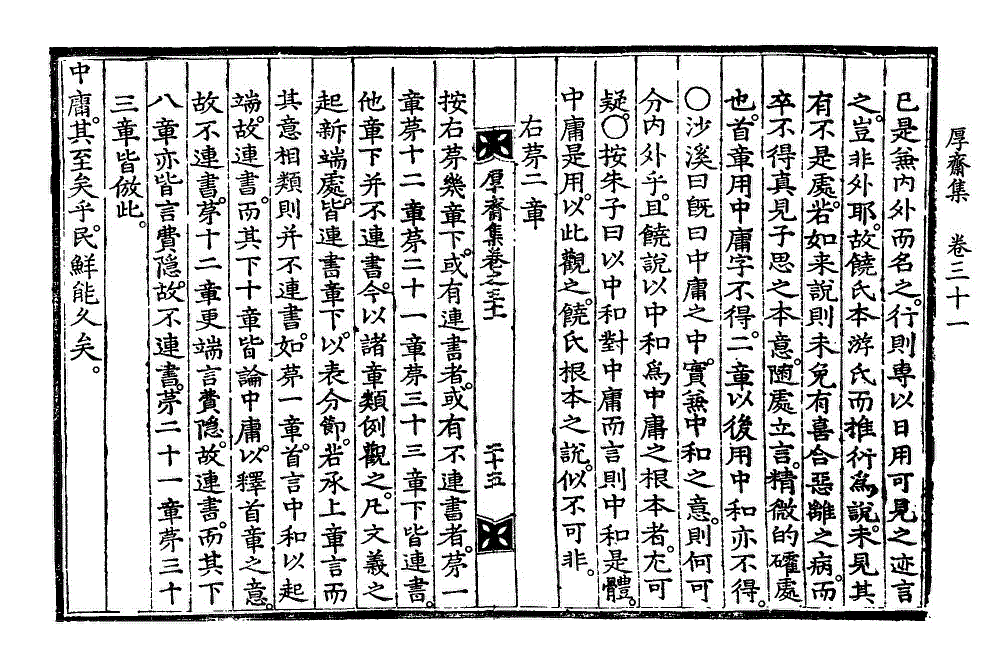 已是兼内外而名之。行则专以日用可见之迹言之。岂非外耶。故饶氏本游氏而推衍为说。未见其有不是处。若如来说则未免有喜合恶离之病。而卒不得真见子思之本意。随处立言。精微的礭处也。首章用中庸字不得。二章以后用中和亦不得。○沙溪曰既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则何可分内外乎。且饶说以中和为中庸之根本者。尤可疑。○按朱子曰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是体。中庸是用。以此观之。饶氏根本之说。似不可非。
已是兼内外而名之。行则专以日用可见之迹言之。岂非外耶。故饶氏本游氏而推衍为说。未见其有不是处。若如来说则未免有喜合恶离之病。而卒不得真见子思之本意。随处立言。精微的礭处也。首章用中庸字不得。二章以后用中和亦不得。○沙溪曰既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则何可分内外乎。且饶说以中和为中庸之根本者。尤可疑。○按朱子曰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是体。中庸是用。以此观之。饶氏根本之说。似不可非。(右第二章)
按右第几章下。或有连书者。或有不连书者。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章下皆连书。他章下并不连书。今以诸章类例观之。凡文义之起新端处。皆连书章下。以表分节。若承上章言而其意相类则并不连书。如第一章。首言中和以起端。故连书。而其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意。故不连书。第十二章更端言费隐。故连书。而其下八章亦皆言费隐。故不连书。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章皆仿此。
[第三章]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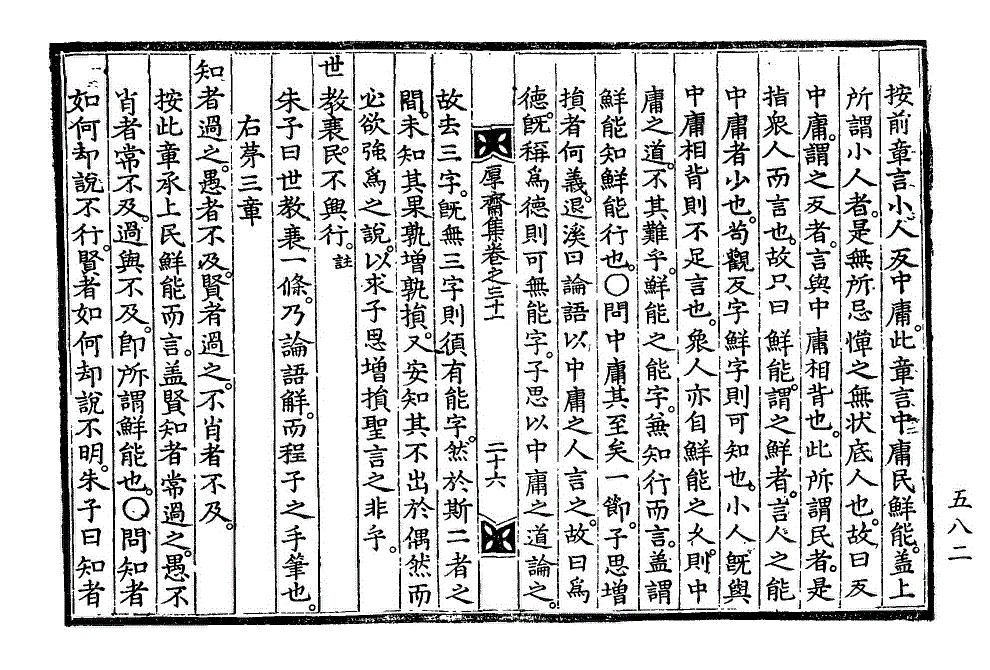 按前章言小。人反中庸。此章言中庸民鲜能。盖上所谓小人者。是无所忌惮之无状底人也。故曰反中庸。谓之反者。言与中庸相背也。此所谓民者。是指众人而言也。故只曰鲜能。谓之鲜者。言人之能中庸者少也。苟观反字鲜字则可知也。小人既与中庸相背则不足言也。众人亦自鲜能之久。则中庸之道。不其难乎。鲜能之能字。兼知行而言。盖谓鲜能知鲜能行也。○问中庸其至矣一节。子思增损者何义。退溪曰论语以中庸之人言之。故曰为德。既称为德则可无能字。子思以中庸之道论之。故去三字。既无三字则须有能字。然于斯二者之间。未知其果孰增孰损。又安知其不出于偶然而必欲强为之说。以求子思增损圣言之非乎。
按前章言小。人反中庸。此章言中庸民鲜能。盖上所谓小人者。是无所忌惮之无状底人也。故曰反中庸。谓之反者。言与中庸相背也。此所谓民者。是指众人而言也。故只曰鲜能。谓之鲜者。言人之能中庸者少也。苟观反字鲜字则可知也。小人既与中庸相背则不足言也。众人亦自鲜能之久。则中庸之道。不其难乎。鲜能之能字。兼知行而言。盖谓鲜能知鲜能行也。○问中庸其至矣一节。子思增损者何义。退溪曰论语以中庸之人言之。故曰为德。既称为德则可无能字。子思以中庸之道论之。故去三字。既无三字则须有能字。然于斯二者之间。未知其果孰增孰损。又安知其不出于偶然而必欲强为之说。以求子思增损圣言之非乎。世教衰。民不兴行。(注)
朱子曰世教衰一条。乃论语解。而程子之手笔也。
(右第三章)
[第四章]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
按此章承上民鲜能而言。盖贤知者常过之。愚不肖者常不及。过与不及。即所谓鲜能也。○问知者如何却说不行。贤者如何却说不明。朱子曰知者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3H 页
 缘他见得过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贤者资质既好。便不去讲学。故曰不明。
缘他见得过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贤者资质既好。便不去讲学。故曰不明。双峰饶氏曰行不是说人去行道。是说道自流行。(止)是说道自著明于天下。(小注)
栗谷曰饶说有病。道之行不行明不明。皆由人也。退溪曰固是人不行道。故道不行。人不明道。故道不明矣。然此所谓不行。指道之不行而言。非谓人不行也。此所谓不明。指道之不明而言。非谓人不明也。饶说精当。不可非之。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按人莫不有日用当行之事。而然知其当行之理者鲜矣。譬如人莫不饮食。而然知其饮食之味者鲜矣。○此鲜能二字。与上文鲜能二字不同。盖上能字实。此能字虚。惟鲜字之意则上下同也。
(右第四章)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
按先言道之不行由于不明。将以起下文舜之大知。所以能行道也。
(右第五章)
[第六章]
舜其大知也与。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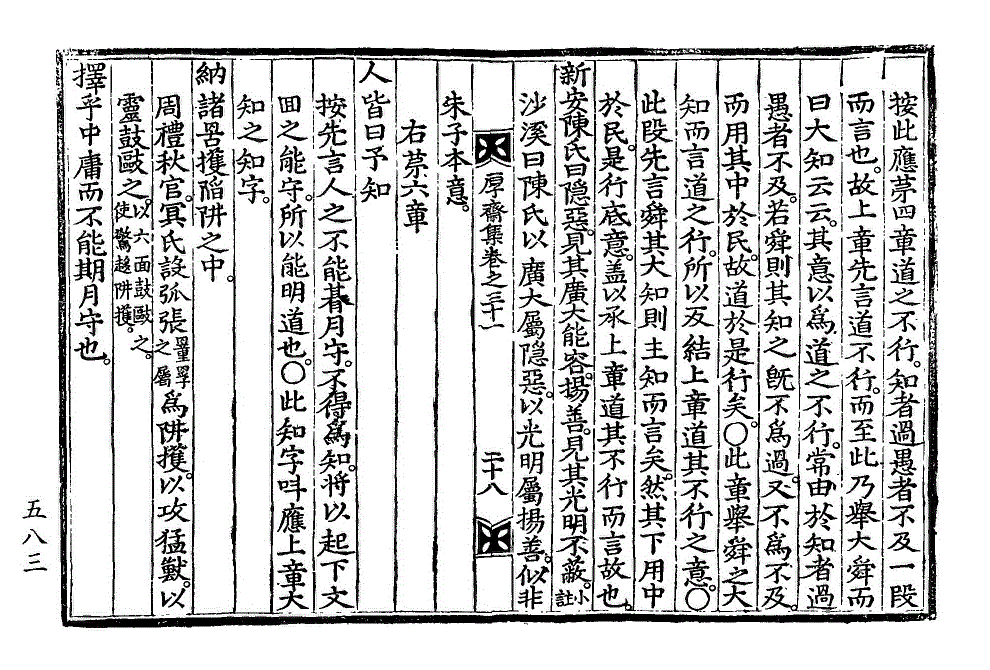 按此应第四章道之不行。知者过愚者不及一段而言也。故上章先言道不行。而至此乃举大舜而曰大知云云。其意以为道之不行。常由于知者过愚者不及。若舜则其知之既不为过。又不为不及。而用其中于民。故道于是行矣。○此章举舜之大知而言道之行。所以反结上章道其不行之意。○此段先言舜其大知则主知而言矣。然其下用中于民。是行底意。盖以承上章道其不行而言故也。
按此应第四章道之不行。知者过愚者不及一段而言也。故上章先言道不行。而至此乃举大舜而曰大知云云。其意以为道之不行。常由于知者过愚者不及。若舜则其知之既不为过。又不为不及。而用其中于民。故道于是行矣。○此章举舜之大知而言道之行。所以反结上章道其不行之意。○此段先言舜其大知则主知而言矣。然其下用中于民。是行底意。盖以承上章道其不行而言故也。新安陈氏曰隐恶。见其广大能容。扬善。见其光明不蔽。(小注)
沙溪曰陈氏以广大属隐恶。以光明属扬善。似非朱子本意。
(右第六章)
[第七章]
人皆曰予知
按先言人之不能期月守。不得为知。将以起下文回之能守。所以能明道也。○此知字叫应上章大知之知字。
纳诸罟获陷阱之中。
周礼秋官。冥氏设弧张(罿罦之属)为阱擭。以攻猛兽。以灵鼓驱之。(以六面鼓驱之。使惊趋阱擭。)
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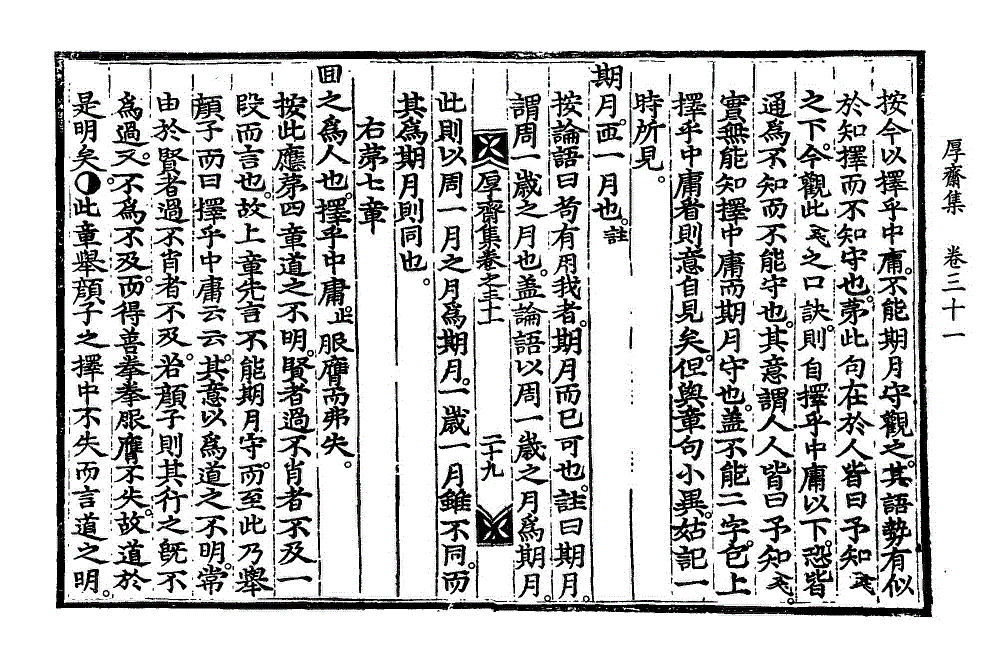 按今以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观之。其语势有似于知择而不知守也。第此句在于人皆曰予知()之下。今观此()之口诀。则自择乎中庸以下。恐皆通为不知而不能守也。其意谓人人皆曰予知()。实无能知择中庸而期月守也。盖不能二字。包上择乎中庸看则意自见矣。但与章句小异。姑记一时所见。
按今以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观之。其语势有似于知择而不知守也。第此句在于人皆曰予知()之下。今观此()之口诀。则自择乎中庸以下。恐皆通为不知而不能守也。其意谓人人皆曰予知()。实无能知择中庸而期月守也。盖不能二字。包上择乎中庸看则意自见矣。但与章句小异。姑记一时所见。期月。匝一月也。(注)
按论语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注曰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盖论语以周一岁之月为期月。此则以周一月之月为期月。一岁一月虽不同。而其为期月则同也。
(右第七章)
[第八章]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止)服膺而弗失。
按此应第四章道之不明。贤者过不肖者不及一段而言也。故上章先言不能期月守。而至此乃举颜子而曰择乎中庸云云。其意以为道之不明。常由于贤者过不肖者不及。若颜子则其行之既不为过。又不为不及。而得善拳拳服膺不失。故道于是明矣。◑此章举颜子之择中不失而言道之明。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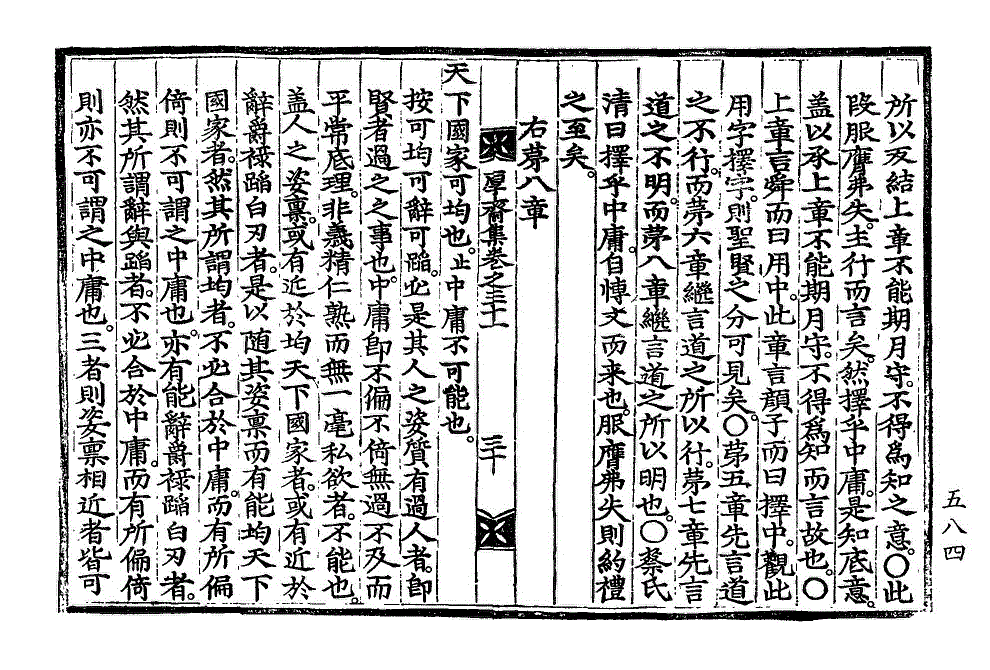 所以反结上章不能期月守。不得为知之意。○此段服膺弗失。主行而言矣。然择乎中庸。是知底意。盖以承上章不能期月守。不得为知而言故也。○上章言舜而曰用中。此章言颜子而曰择中。观此用字择字。则圣贤之分可见矣。○第五章先言道之不行。而第六章继言道之所以行。第七章先言道之不明。而第八章继言道之所以明也。○蔡氏清曰择乎中庸。自博文而来也。服膺弗失则约礼之至矣。
所以反结上章不能期月守。不得为知之意。○此段服膺弗失。主行而言矣。然择乎中庸。是知底意。盖以承上章不能期月守。不得为知而言故也。○上章言舜而曰用中。此章言颜子而曰择中。观此用字择字。则圣贤之分可见矣。○第五章先言道之不行。而第六章继言道之所以行。第七章先言道之不明。而第八章继言道之所以明也。○蔡氏清曰择乎中庸。自博文而来也。服膺弗失则约礼之至矣。(右第八章)
[第九章]
天下国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
按可均可辞可蹈。必是其人之姿质有过人者。即贤者过之之事也。中庸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底理。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私欲者。不能也。盖人之姿禀。或有近于均天下国家者。或有近于辞爵禄蹈白刃者。是以随其姿禀而有能均天下国家者。然其所谓均者。不必合于中庸。而有所偏倚则不可谓之中庸也。亦有能辞爵禄蹈白刃者。然其所谓辞与蹈者。不必合于中庸。而有所偏倚则亦不可谓之中庸也。三者则姿禀相近者皆可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5H 页
 能之。惟中庸则非只是姿禀相近者。所可勉而能之。此所以三者可能。而中庸不可能也。虽然所谓中庸者。不是舍此三者而别求一个物也。只三者之合道理恰好处。便是中庸也。○上章言鲜能。此章言不可能。所谓鲜能者。只是言人于中庸。能之者鲜而已。所谓不可能者。言中庸至难而不可能也。比鲜能有加焉耳。○此亦先言中庸不可能。以起下文子路之问强。
能之。惟中庸则非只是姿禀相近者。所可勉而能之。此所以三者可能。而中庸不可能也。虽然所谓中庸者。不是舍此三者而别求一个物也。只三者之合道理恰好处。便是中庸也。○上章言鲜能。此章言不可能。所谓鲜能者。只是言人于中庸。能之者鲜而已。所谓不可能者。言中庸至难而不可能也。比鲜能有加焉耳。○此亦先言中庸不可能。以起下文子路之问强。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注)
按苟有一毫私欲之未祛。则所谓中庸者。为此私欲所蔽。终不能合于道理之当然。而有过不及之弊也。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注)
按上章言择乎中庸。而此章言中庸不可能也。此章言中庸不可能。而下章言中立不倚。强哉矫。则其所以承上章起下章之意可见矣。
(右第九章)
[第十章]
子路问强。
按上章蹈白刃。即勇也。此强字应勇底意。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止)君子居之。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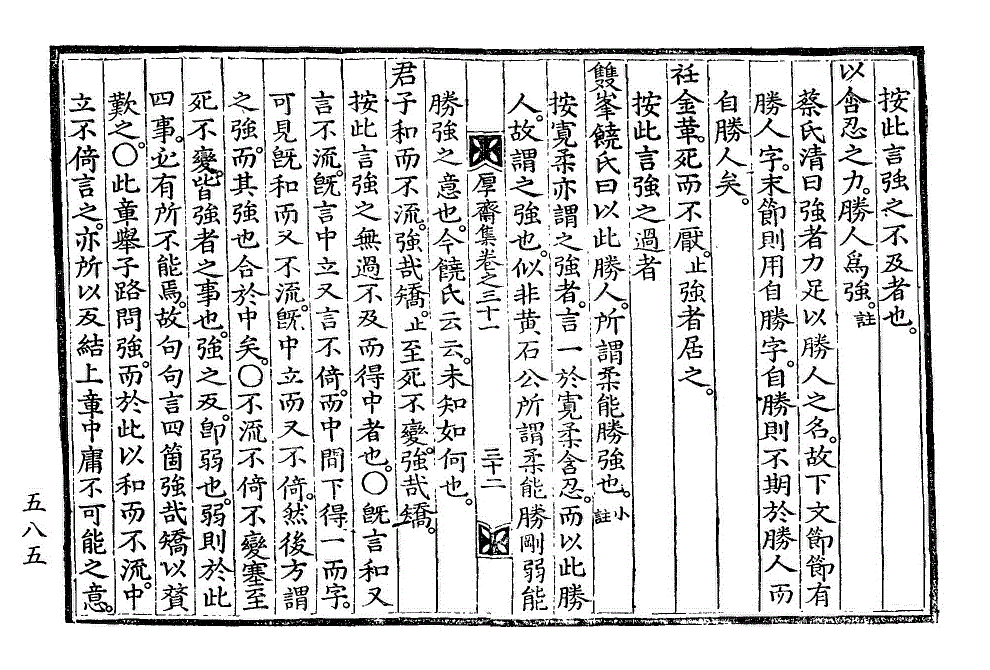 按此言强之不及者也。
按此言强之不及者也。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注)
蔡氏清曰强者力足以胜人之名。故下文节节有胜人字。末节则用自胜字。自胜则不期于胜人而自胜人矣。
衽金革。死而不厌。(止)强者居之。
按此言强之过者。
双峰饶氏曰以此胜人。所谓柔能胜强也。(小注)
按宽柔亦谓之强者。言一于宽柔含忍。而以此胜人。故谓之强也。似非黄石公所谓柔能胜刚弱能胜强之意也。今饶氏云云。未知如何也。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止)至死不变。强哉矫。
按此言强之无过不及而得中者也。○既言和又言不流。既言中立又言不倚。而中问下得一而字。可见既和而又不流。既中立而又不倚。然后方谓之强。而其强也合于中矣。○不流不倚不变塞至死不变。皆强者之事也。强之反。即弱也。弱则于此四事。必有所不能焉。故句句言四个强哉矫以赞叹之。○此章举子路问强。而于此以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言之。亦所以反结上章中庸不可能之意。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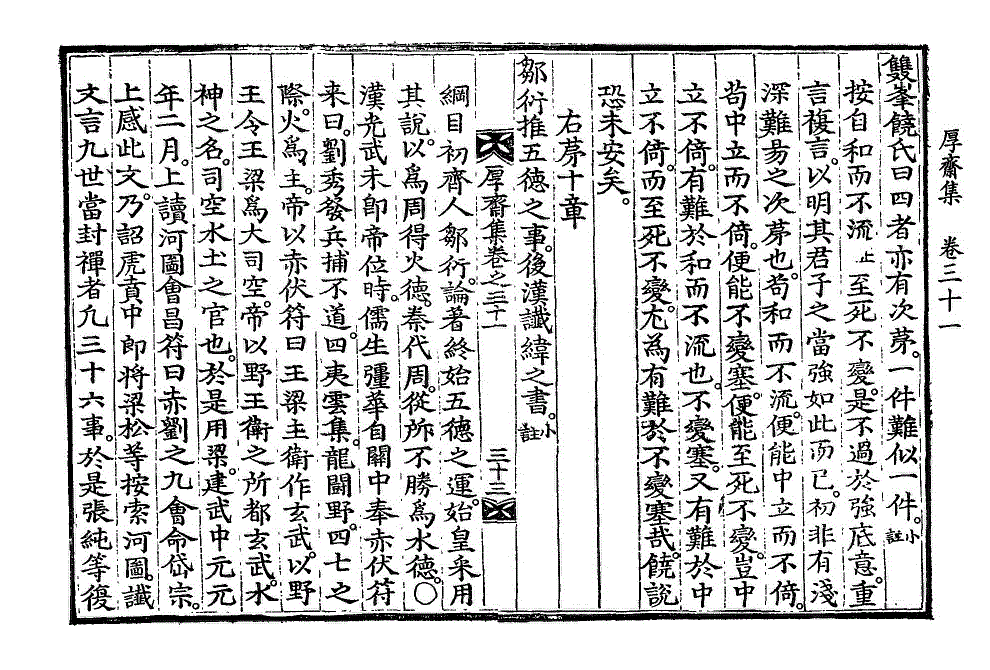 双峰饶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难似一件。(小注)
双峰饶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难似一件。(小注)按自和而不流(止)至死不变。是不过于强底意。重言复言。以明其君子之当强如此而已。初非有浅深难易之次第也。苟和而不流。便能中立而不倚。苟中立而不倚。便能不变塞。便能至死不变。岂中立不倚。有难于和而不流也。不变塞。又有难于中立不倚。而至死不变。尤为有难于不变塞哉。饶说恐未安矣。
(右第十章)
[第十一章]
邹衍推五德之事。后汉谶纬之书。(小注)
纲目初齐人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汉光武未即帝位时。儒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帝以野王卫之所都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用梁。建武中元元年二月。上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诏虎贲中郎将梁松等按索河图。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张纯等复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6L 页
 奏请封禅。上许焉。十一月宣布图谶于天下。
奏请封禅。上许焉。十一月宣布图谶于天下。荀子所谓苟难。于陵仲子,申屠狄尾生。(小注)
荀子曰君子行不贵苟难。○陈仲子见孟子。○申屠狄夏时贤人。汤以天下授之。耻不以义闻。已自投于河。○尾生鲁之信人。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不能已矣。
按既曰遵道而行则知之能择矣。又曰半涂而废则是仁不能守矣。只是当勇而不勇矣。盖以不勇故。于道虽知遵行。而不能勉而进之。以求合乎中。而径自废焉。
君子依乎中庸。(止)圣者能之。
按索隐。知之过也。行怪。行之过也。遵道行半涂废。是知及而行不逮也。依乎中庸遁。世不悔。是知行之无过不及。而并合乎中者也。○夫子于索隐行怪。曰吾不为。于半涂而废曰吾不能已。皆言吾字。独于遁世不悔则不言吾。而只曰惟圣者能之。何也。盖上两事。或过或不及。不合于圣人中庸之道。故夫子直自担当曰吾不为吾不能已也。此一事。非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合乎中者不能。此为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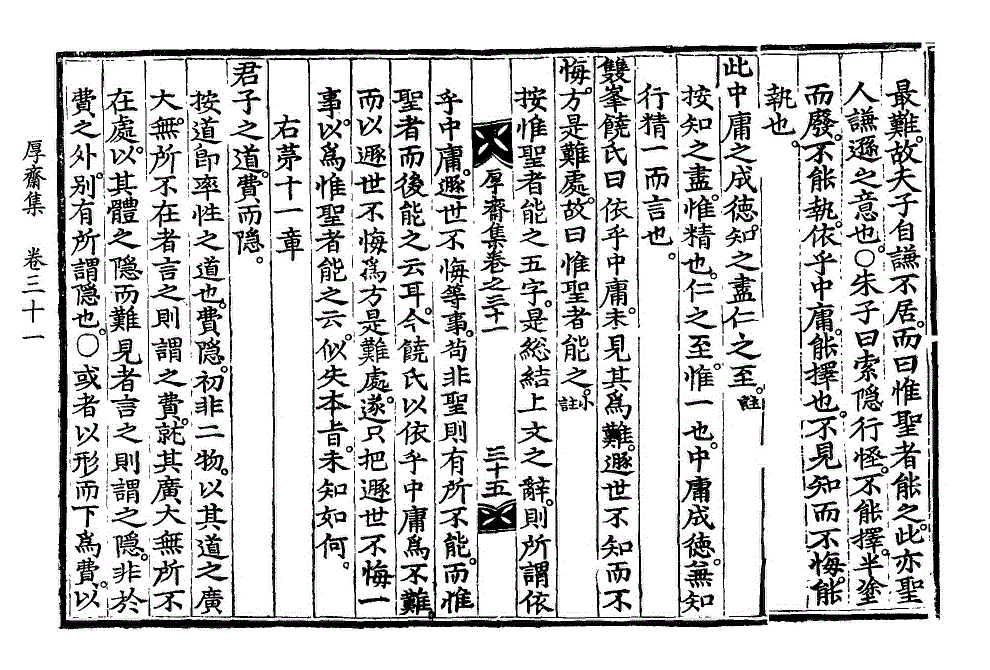 最难。故夫子自谦不居。而曰惟圣者能之。此亦圣人谦逊之意也。○朱子曰索隐行怪。不能择。半涂而废。不能执。依乎中庸。能择也。不见知而不悔。能执也。
最难。故夫子自谦不居。而曰惟圣者能之。此亦圣人谦逊之意也。○朱子曰索隐行怪。不能择。半涂而废。不能执。依乎中庸。能择也。不见知而不悔。能执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尽仁之至。(注)
按知之尽。惟精也。仁之至。惟一也。中庸成德。兼知行精一而言也。
双峰饶氏曰依乎中庸。未见其为难。遁世不知而不悔。方是难处。故曰惟圣者能之。(小注)
按惟圣者能之五字。是总结上文之辞。则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悔等事。苟非圣则有所不能。而惟圣者而后能之云耳。今饶氏以依乎中庸为不难。而以遁世不悔为方是难处。遂只把遁世不悔一事。以为惟圣者能之云。似失本旨。未知如何。
(右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
按道即率性之道也。费隐。初非二物。以其道之广大。无所不在者言之则谓之费。就其广大无所不在处。以其体之隐而难见者言之则谓之隐。非于费之外。别有所谓隐也。○或者以形而下为费。以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7L 页
 形而上为隐。此说不是。盖形而下者。非费也。凡形而下之物。莫不各具其理。而理无所不在者。所谓费也。然所谓费之体。有非视听所及者。故曰隐也。然则费与隐。皆形而上者。而从无所不在处说则谓之费。从视听所不及处说则谓之隐也。○蔡氏清曰自古圣贤。论道者多矣。未有如子思费隐一章之精妙而该括者也。
形而上为隐。此说不是。盖形而下者。非费也。凡形而下之物。莫不各具其理。而理无所不在者。所谓费也。然所谓费之体。有非视听所及者。故曰隐也。然则费与隐。皆形而上者。而从无所不在处说则谓之费。从视听所不及处说则谓之隐也。○蔡氏清曰自古圣贤。论道者多矣。未有如子思费隐一章之精妙而该括者也。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止)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按夫妇之愚不肖。皆可以知行者。道也。圣人天地之亦有所不能者。亦道也。可见道之无所不在矣。此则费也。然其所以然者。是隐也。○及其至也此至字。非精妙极至之谓也。圣人岂不知道之精妙极至处耶。凡天地间事事物物。千头万绪。千形万色。莫不有道存焉。所谓至者。举此包括。无一或遗之谓也。故虽圣人或有所不知不能也。夫妇之愚不肖而所能知能行者。如爱亲慈子饥食渴饮之类。虽至愚之人。亦能知能行矣。○以天地之大。犹有不能尽者。而未免于人之有所憾焉。则道之至大至广者。于此亦可见矣。此所谓道之费也。○莫能载者。只是形容道之至大也。莫能破者。只是形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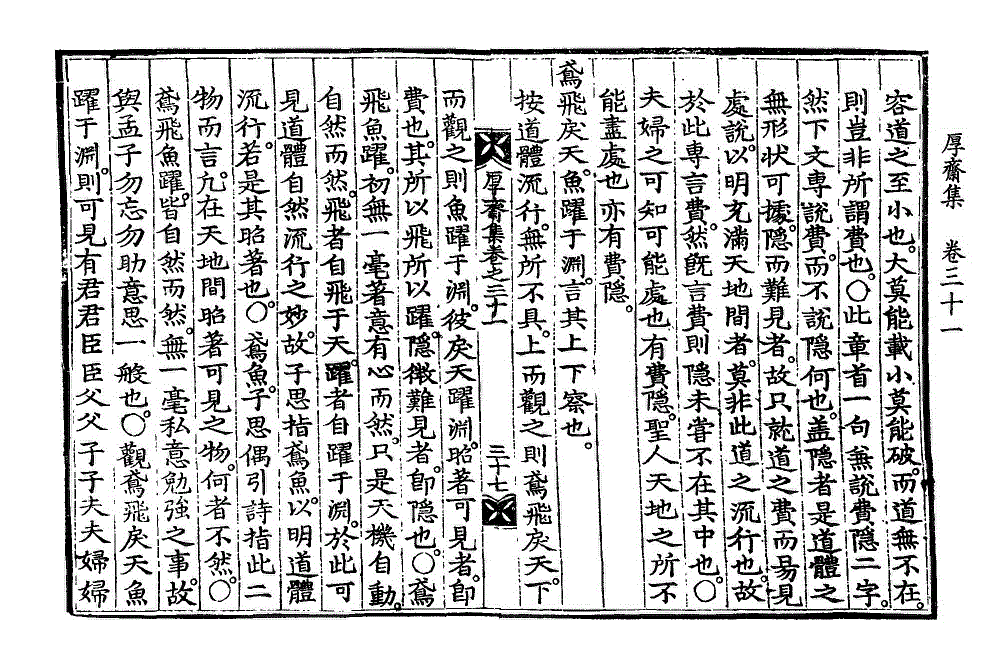 容道之至小也。大莫能载小莫能破。而道无不在。则岂非所谓费也。○此章首一句兼说费隐二字。然下文专说费。而不说隐何也。盖隐者是道体之无形状可据。隐而难见者。故只就道之费而易见处说。以明充满天地间者。莫非此道之流行也。故于此专言费。然既言费则隐未尝不在其中也。○夫妇之可知可能处也有费隐。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处也亦有费隐。
容道之至小也。大莫能载小莫能破。而道无不在。则岂非所谓费也。○此章首一句兼说费隐二字。然下文专说费。而不说隐何也。盖隐者是道体之无形状可据。隐而难见者。故只就道之费而易见处说。以明充满天地间者。莫非此道之流行也。故于此专言费。然既言费则隐未尝不在其中也。○夫妇之可知可能处也有费隐。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处也亦有费隐。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
按道体流行。无所不具。上而观之则鸢飞戾天。下而观之则鱼跃于渊。彼戾天跃渊。昭著可见者。即费也。其所以飞所以跃。隐微难见者。即隐也。○鸢飞鱼跃。初无一毫著意有心而然。只是天机自动。自然而然。飞者自飞于天。跃者自跃于渊。于此可见道体自然流行之妙。故子思指鸢鱼。以明道体流行。若是其昭著也。○鸢鱼。子思偶引诗指此二物而言。凡在天地间昭著可见之物。何者不然。○鸢飞鱼跃。皆自然而然。无一毫私意勉强之事。故与孟子勿忘勿助意思一般也。○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则可见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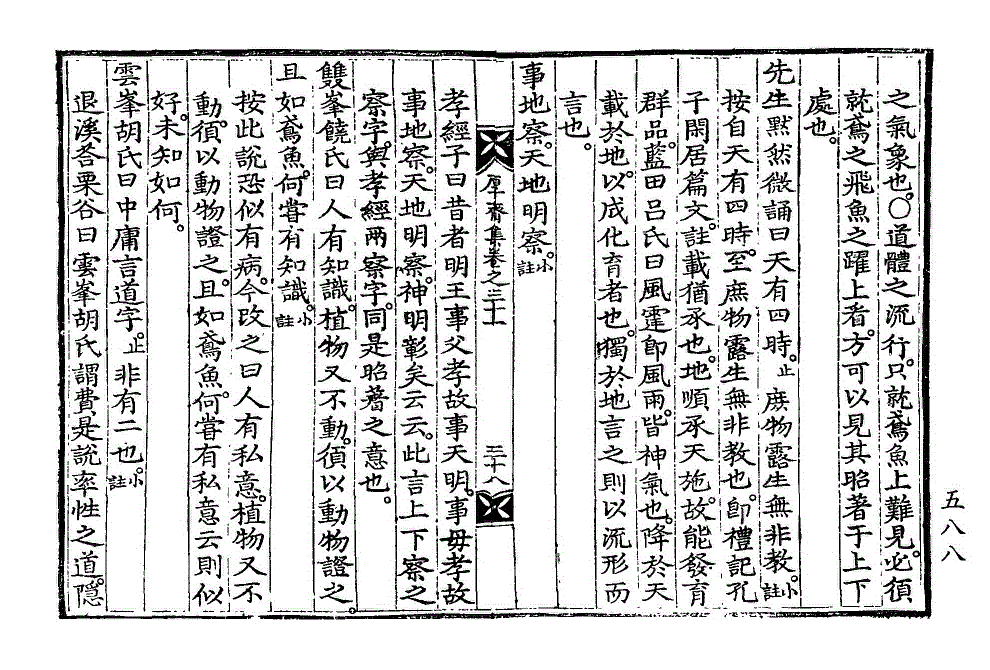 之气象也。○道体之流行。只就鸢鱼上难见。必须就鸢之飞鱼之跃上看。方可以见其昭著于上下处也。
之气象也。○道体之流行。只就鸢鱼上难见。必须就鸢之飞鱼之跃上看。方可以见其昭著于上下处也。先生默然微诵曰天有四时。(止)庶物露生无非教。(小注)
按自天有四时。至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即礼记孔子闲居篇文。注载犹承也。地顺承天施。故能发育群品。蓝田吕氏曰风霆即风雨。皆神气也。降于天载于地。以成化育者也。独于地言之则以流形而言也。
事地察。天地明察。(小注)
孝经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云云。此言上下察之察字。与孝经两察字。同是昭著之意也。
双峰饶氏曰人有知识。植物又不动。须以动物證之。且如鸢鱼。何尝有知识。(小注)
按此说恐似有病。今改之曰人有私意。植物又不动。须以动物證之。且如鸢鱼。何尝有私意云则似好。未知如何。
云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止)非有二也。(小注)
退溪答栗谷曰云峰胡氏谓费是说率性之道。隐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9H 页
 是说天命之性。若单说此二句。亦似衍说。第云峰此段。乃铺说一篇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说来。故其说不得不如此。正如朱子或问通论诚处。直自天命之性说起来也。恐无害也。
是说天命之性。若单说此二句。亦似衍说。第云峰此段。乃铺说一篇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说来。故其说不得不如此。正如朱子或问通论诚处。直自天命之性说起来也。恐无害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止)察乎天地。
按道即所谓费隐之道也。盖道体以上下之昭著者言则莫如鸢鱼。而以人事之至近者言则莫如夫妇。故于此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言造道之端。自夫妇间戒谨处始也。造端如云始事也。盖夫妇之间。至亲至密。人所易亵。幽暗之中。衽席之上。或有一毫不谨则道体有所不行。故特举夫妇而言。以见其造道自尤切近处始也。○君子之道。始为造端于夫妇居室之间。而及其极至处。流行遍满。昭著充塞于天地之大也。此则所谓费也。○夫妇二字。与上文夫妇应。但上文夫妇之与知能行者。以道中之一事言。此造端乎夫妇者。以造道之始事言。上言道体之易见处。此言道体之至近处。○沙溪曰造端是托始之意。君子之道。托始于近小夫妇居室之间。乃至理流行至极处。昭著于天地之际。无非此道之呈露。此夫妇与上文愚夫
厚斋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第 5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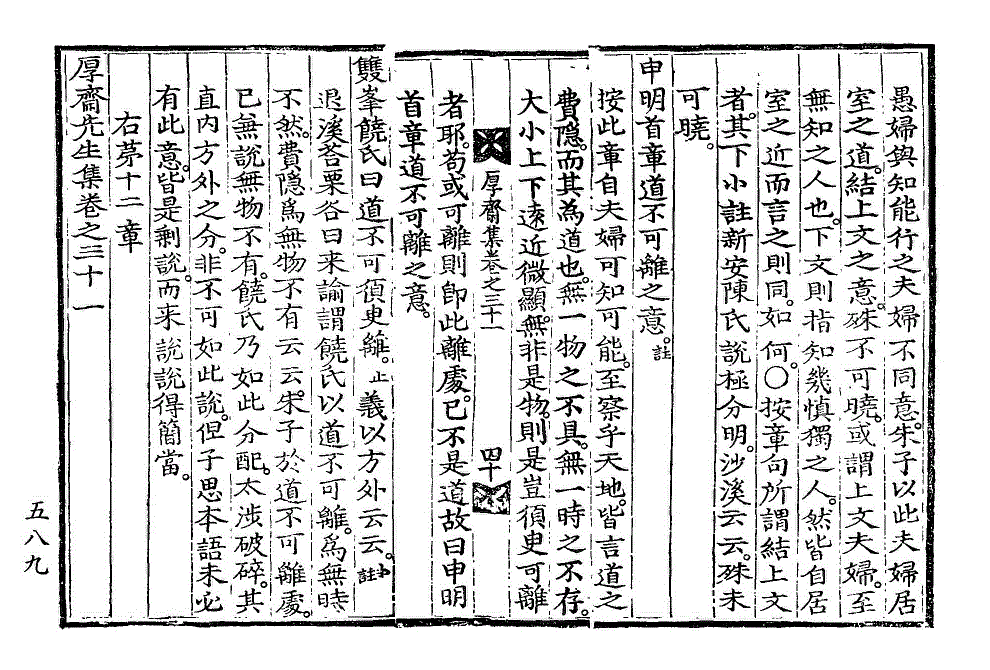 愚妇与知能行之夫妇不同意。朱子以此夫妇居室之道。结上文之意。殊不可晓。或谓上文夫妇。至无知之人也。下文则指知几慎独之人。然皆自居室之近而言之则同。如何。○按章句所谓结上文者。其下小注新安陈氏说极分明。沙溪云云。殊未可晓。
愚妇与知能行之夫妇不同意。朱子以此夫妇居室之道。结上文之意。殊不可晓。或谓上文夫妇。至无知之人也。下文则指知几慎独之人。然皆自居室之近而言之则同。如何。○按章句所谓结上文者。其下小注新安陈氏说极分明。沙溪云云。殊未可晓。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注)
按此章自夫妇可知可能。至察乎天地。皆言道之费隐。而其为道也。无一物之不具。无一时之不存。大小上下远近微显。无非是物。则是岂须臾可离者耶。苟或可离则即此离处。已不是道故曰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
双峰饶氏曰道不可须臾离。(止)义以方外云云。(小注)
退溪答栗谷曰来谕谓饶氏以道不可离。为无时不然。费隐为无物不有云云。朱子于道不可离处。已兼说无物不有。饶氏乃如此分配。太涉破碎。其直内方外之分。非不可如此说。但子思本语未必有此意。皆是剩说。而来说说得简当。
(右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