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x 页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劄记○孟子
劄记○孟子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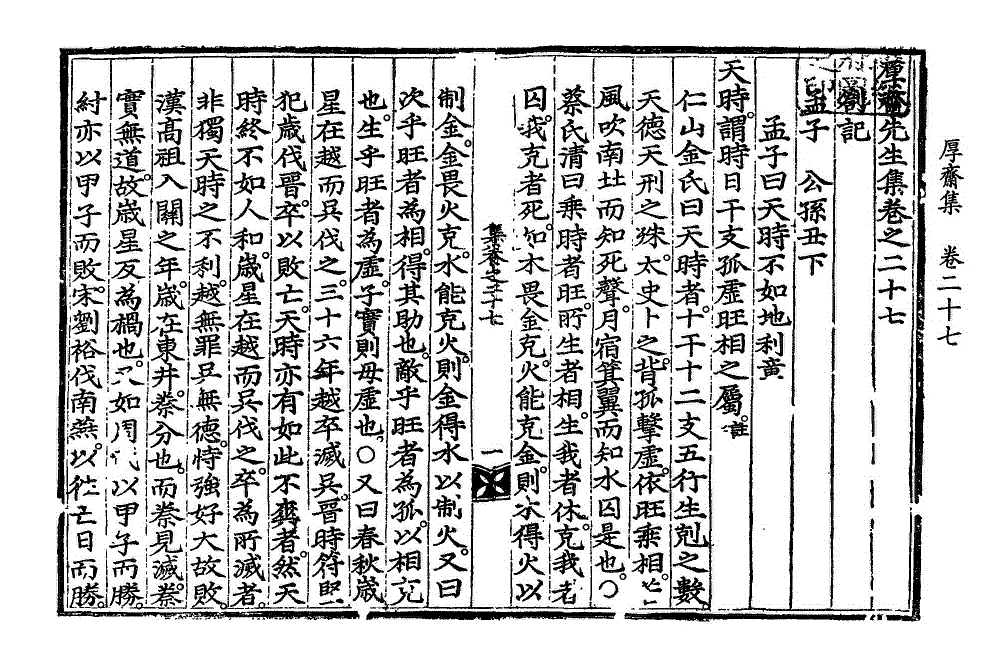 公孙丑下
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章
天时。谓时日干支孤虚旺相之属。(注)
仁山金氏曰天时者。十干十二支五行生剋之数。天德天刑之殊。太史卜之。背孤击虚。依旺乘相。若风吹南北而知死声。月宿箕翼而知水囚是也。○蔡氏清曰乘时者旺。所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如木畏金克。火能克金。则木得火以制金。金畏火克。水能克火。则金得水以制火。又曰次乎旺者为相。得其助也。敌乎旺者为孤。以相克也。生乎旺者为虚。子实则母虚也。○又曰春秋岁星在越而吴伐之。三十六年越卒灭吴。晋时符坚犯岁伐晋。卒以败亡。天时亦有如此不爽者。然天时终不如人和。岁星在越而吴伐之。卒为所灭者。非独天时之不利。越无罪吴无德。恃强好大故败。汉高祖入关之年。岁在东井。秦分也。而秦见灭。秦实无道。故岁星反为祸也。又如周代以甲子而胜。纣亦以甲子而败。宋刘裕伐南燕。以往亡日而胜。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88L 页
 故曰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闇将拘之。
故曰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闇将拘之。蔡氏曰时。四时也。(小注)
按时非但四时。十二时亦在其中也。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止)天下顺之。
按此一节。专以得民心为重而言。盖既得民心则天下之人皆悦而愿为之氓。不必以封疆之界为限也。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亦可以坚守。不必以溪山之险为固也。德教刑政。及于天下。则民自畏之。不必以兵革之坚利为威也。得道者。所谓得民心之和者也。失道者。即失民心之和者也。非民心和不和之外。别有得失之道也。得民心之和者多助。而极其效则至于天下之人顺之。失民心之和者寡助。而极其效则虽亲戚之人亦畔之。
孟子将朝王章
朱子曰有事则王自来见。或自往见。(小注)
按王自来见。言王自来见贤者。或自往见。言贤者或自往见王也。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止)如之何不吊。
按孟子之出吊东郭。岂无他日。必以其明日者。盖与孔子不见孺悲。取瑟而歌者同。其意可谓微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89H 页
 公孙丑不知此意。乃以昨辞疾今出吊为嫌。而曰或者不可。故孟子于此。不欲质言其微意。只答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其言可谓雍容含蓄。真圣人之言也。至景丑氏之问。又有不得不明言以晓者。故方始引曾子之说以言之也。
公孙丑不知此意。乃以昨辞疾今出吊为嫌。而曰或者不可。故孟子于此。不欲质言其微意。只答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其言可谓雍容含蓄。真圣人之言也。至景丑氏之问。又有不得不明言以晓者。故方始引曾子之说以言之也。王使人问疾医来。(止)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按仲子不知孟子之微意。故乃反欲周遮其托疾出吊之迹。而为此权辞。且有要路造朝之请。使孟子致有不得已而之景丑氏之举也。○又按孟氏谱云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三迁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此二说与赵氏说不同。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止)莫如我敬王也。
按见王之敬子。即如上文所谓寡人如就见及使人问疾医来等事是也。未见所以敬王。即如下文所谓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之事是也。上言仁义二字。而下又变言尧舜之道何也。盖尧舜之道。不出于仁义而已也。○景子既以孟子为未敬王。故孟子乃言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不敬莫大乎是。所谓齐人二字。虽似不为专指景子而言。然所以折景子之意。分明包在其中。○蔡氏清曰欲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89L 页
 归则以仲子之要而势有不获。欲往则以齐王之召而义有不可。是为不得已也。
归则以仲子之要而势有不获。欲往则以齐王之召而义有不可。是为不得已也。景子曰非此之谓。
按非此之此。即指上文仁义尧舜之道等事而言也。
曰岂谓是欤。
按是字即指景子所引礼说也。盖景子只知事君有承召趋走之礼。而不知此外又有别样道理。故遂引曾子之说以告之也。
东阳许氏曰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义字不同。(小注)
按曾,思,孟三夫子平日所言者。皆是仁义。故曾子于此。亦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于富言仁。于爵言义。是泛说耳。虽互言亦得。初非富在彼故言仁。爵加我故言义也。许说恐失本旨。
陈臻问曰章
予有戒心
按戒即戒备也。如所谓戒严。
若于齐则未有处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0H 页
 按无处二字。或以齐王看。谓齐王之馈为无处也。或以孟子看。谓孟子以无处之物而辞之也。然此两说只是一意。不可偏属一边也。盖齐王以无处而馈之。故孟子亦以无处而不受。集注曰无远行戒心之事。是未有处也。夫无远行戒心而馈之则是其馈为无处也。无远行戒心而受之则是其受亦为无处也。
按无处二字。或以齐王看。谓齐王之馈为无处也。或以孟子看。谓孟子以无处之物而辞之也。然此两说只是一意。不可偏属一边也。盖齐王以无处而馈之。故孟子亦以无处而不受。集注曰无远行戒心之事。是未有处也。夫无远行戒心而馈之则是其馈为无处也。无远行戒心而受之则是其受亦为无处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按集注曰取。犹致也。今若无处而馈君子则是货之也。此非以君子致君子也。便是以货致君子也。岂有君子。而可以货致之耶。
孟子之平陆章
大夫邑宰也(注)
册府元龟曰鲁谓之宰。仲尼为中都宰是也。齐谓之大夫。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谓之尹。沈尹戍为方城之外县尹是也。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按子之失伍。即下文所谓老羸填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者。其意盖欲委罪于王。即应章末此则寡人之罪一句。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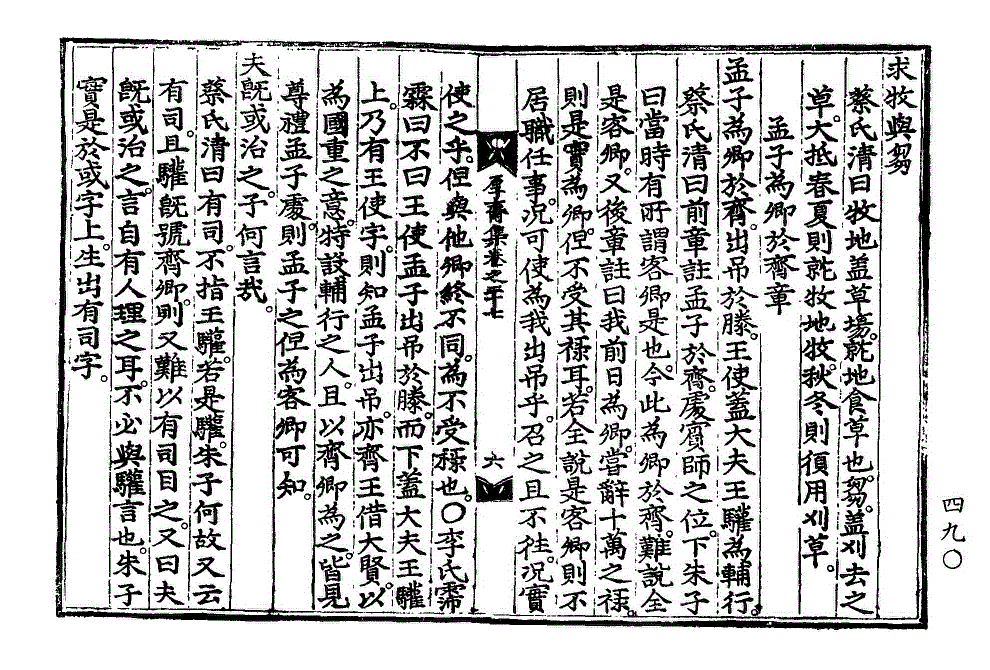 求牧与刍
求牧与刍蔡氏清曰牧地盖草场。就地食草也。刍。盖刈去之草。大抵春夏则就牧地牧。秋冬则须用刈草。
孟子为卿于齐章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
蔡氏清曰前章注孟子于齐。处宾师之位。下朱子曰当时有所谓客卿是也。今此为卿于齐。难说全是客卿。又后章注曰我前日为卿。尝辞十万之禄。则是实为卿。但不受其禄耳。若全说是客卿则不居职任事。况可使为我出吊乎。召之且不往。况实使之乎。但与他卿终不同。为不受禄也。○李氏霈霖曰不曰王使孟子出吊于滕。而下盖大夫王驩上。乃有王使字。则知孟子出吊。亦齐王借大贤。以为国重之意。特设辅行之人。且以齐卿为之。皆见尊礼孟子处。则孟子之但为客卿可知。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蔡氏清曰有司。不指王驩。若是驩。朱子何故又云有司。且驩既号齐卿。则又难以有司目之。又曰夫既或治之。言自有人理之耳。不必与驩言也。朱子实是于或字上。生出有司字。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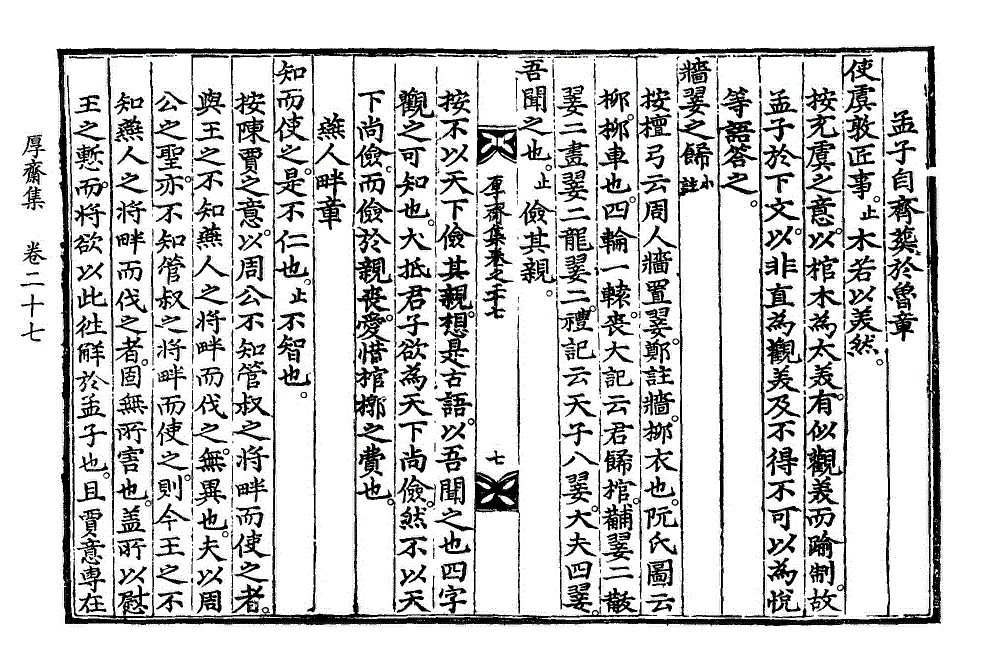 孟子自齐葬于鲁章
孟子自齐葬于鲁章使虞敦匠事。(止)木若以美然。
按充虞之意。以棺木为太美。有似观美而踰制。故孟子于下文。以非直为观美及不得不可以为悦等语答之。
墙翣之饰(小注)
按檀弓云周人墙置翣。郑注墙。柳衣也。阮氏图云柳。柳车也。四轮一辕。丧大记云君饰棺。黼翣二 黻翣二 画翣二 龙翣二。礼记云天子八翣。大夫四翣。
吾闻之也。(止)俭其亲。
按不以天下俭其亲。想是古语。以吾闻之也四字观之可知也。大抵君子欲为天下尚俭。然不以天下尚俭。而俭于亲丧。爱惜棺椁之费也。
燕人畔章
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止)不智也。
按陈贾之意。以周公不知管叔之将畔而使之者。与王之不知燕人之将畔而伐之。无异也。夫以周公之圣。亦不知管叔之将畔而使之。则今王之不知燕人之将畔而伐之者。固无所害也。盖所以慰王之惭。而将欲以此往解于孟子也。且贾意专在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1L 页
 于不智二字上。故下文只举知其将畔而使之欤以为问。
于不智二字上。故下文只举知其将畔而使之欤以为问。今之君子。过则顺之。
按以集注所谓责贾不能勉其君以迁善改过。而教之以遂非文过等语观之。则今之君子过则顺之者。似指陈贾而言也。至其下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其所以深责陈贾者。尤为分明矣。
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
按其过也下既有如日月之食五字。则及其更也下亦以如日月之明意看。尤似分晓。
孟子致为臣而归章
孟子致为臣而归
按致字。如致仕之致。孟子既为卿于齐。今曰致为臣而归者。是还致其卿位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
按他日。非久远之谓。苟非齐王就见之日。虽在明日。亦可谓之他日。如上章以昨日疾。谓昔者之类也。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
按此然字。盖孟子未尝知齐王有授室养禄之意。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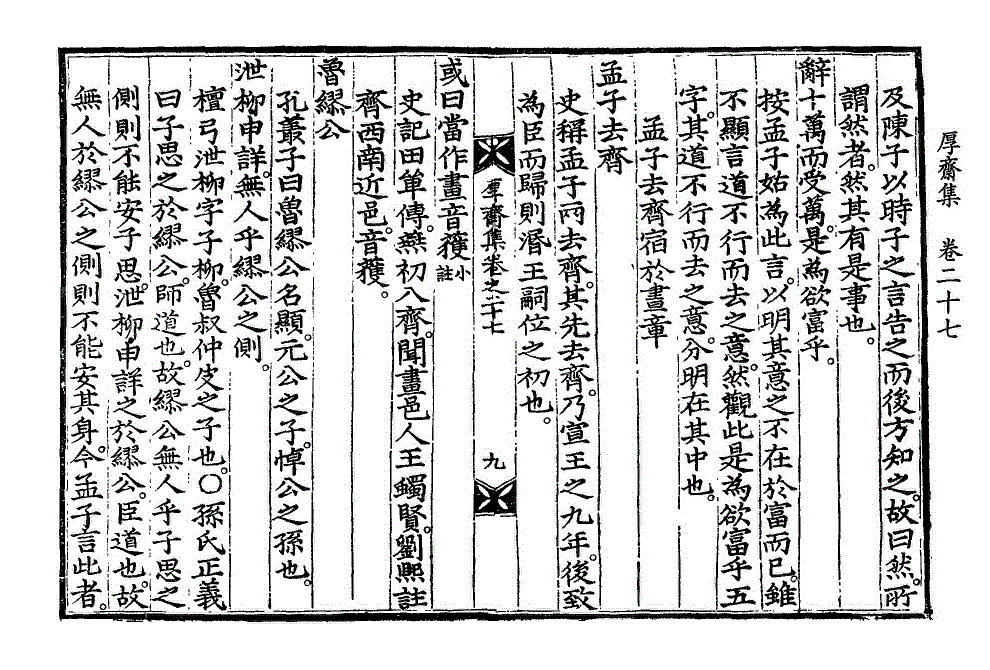 及陈子以时子之言告之而后方知之。故曰然。所谓然者。然其有是事也。
及陈子以时子之言告之而后方知之。故曰然。所谓然者。然其有是事也。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按孟子姑为此言。以明其意之不在于富而已。虽不显言道不行而去之意。然观此是为欲富乎五字。其道不行而去之意。分明在其中也。
孟子去齐宿于昼章
孟子去齐
史称孟子两去齐。其先去齐。乃宣王之九年。后致为臣而归则湣王嗣位之初也。
或曰当作画音获(小注)
史记田单传。燕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刘熙注齐西南近邑。音获。
鲁缪公
孔丛子曰鲁缪公名显。元公之子。悼公之孙也。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
檀弓泄柳字子柳。鲁叔仲皮之子也。○孙氏正义曰子思之于缪公。师道也。故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之于缪公。臣道也。故无人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今孟子言此者。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2L 页
 是齐之士不能为王谋安于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昼然后方为留行。此所以隐几卧而不答也。
是齐之士不能为王谋安于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昼然后方为留行。此所以隐几卧而不答也。子为长者虑。(止)长者绝子乎。
蔡氏清曰全在为长者虑不及子思一句上。正为缪公是自使人于子思之侧。今齐王不使子来。而子自欲为王留我。则不以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绝子也。○按所谓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者。其言有若疑辞。而其意实深责子之绝我也。今蔡氏曰宜乎我之绝子。恐失本旨。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章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止)是何濡滞也。士则玆不悦。
蔡氏清曰尹士讥孟子为三段。一曰是不明也。二曰是干泽也。三乃曰是何濡滞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滞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也。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即如此说。便见不敢逆以为不足为汤武。且非干泽之意尤明矣。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蔡氏清曰尹士最有功于孟子。当时若无尹士之讥评。无以发孟子之本心。七篇中所载诸人。与孟子相辨论者。皆无如尹士之优柔而深切。主于义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3H 页
 理而不主于势利。其人品为独高也。且闻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责已曰士诚小人也。呜呼。尹士其诚君子哉。
理而不主于势利。其人品为独高也。且闻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责已曰士诚小人也。呜呼。尹士其诚君子哉。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章。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按以下文结语吾何为不豫观之。则孟子之实未尝有不豫者可知也。然以彼一时此一时之意观之。则孟子于此。亦不能无不豫矣。盖孟子当战国昏乱之时。抱命世经济之具。而幸而遇齐宣足用为善之资。庶几可以行道救民矣。而今又不遇而去。则孟子亦安得无不豫哉。然则孟子之不豫者。非只以不遇为不豫也。以道不行故为不豫也。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按彼一时。是不怨尤之时也。此一时。是有不豫色之时也。盖所遇之时不同。则所处之道。亦随而异也。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按孟子至此。显以名世者自当。无复谦辞也。此与上章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者。其意同。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3L 页
 孟子去齐居休章
孟子去齐居休章庆源辅氏曰礼则有常。义则有权。(小注)
按礼常之外。非别有所谓义权也。只是就礼常中以义权之也。如君命召不俟驾。是礼之常也。然有不召之臣。故孟子不朝齐王而辞以病。即是就礼上以义权之。而使得其礼之宜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章
滕文公为世子
按或以为天子之子谓之太子。诸侯之子谓之世子。然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称世子。则古者世子太子通称而无别。自汉世乃分天子之子为太子。诸侯之子为世子。
孟子道性善
按孟子对梁惠王言仁义。对滕世子道性善。仁义性善。自是一事。盖性善。即仁义也。
程子曰凡言善恶。(止)先是后非。(注)
按程子此言。是大纲说也。如阴阳先阴而后阳。如祸福先祸而后福。如忧乐先忧而后乐。如死生先死而后生。以此言之。程子之言。恐不可泥看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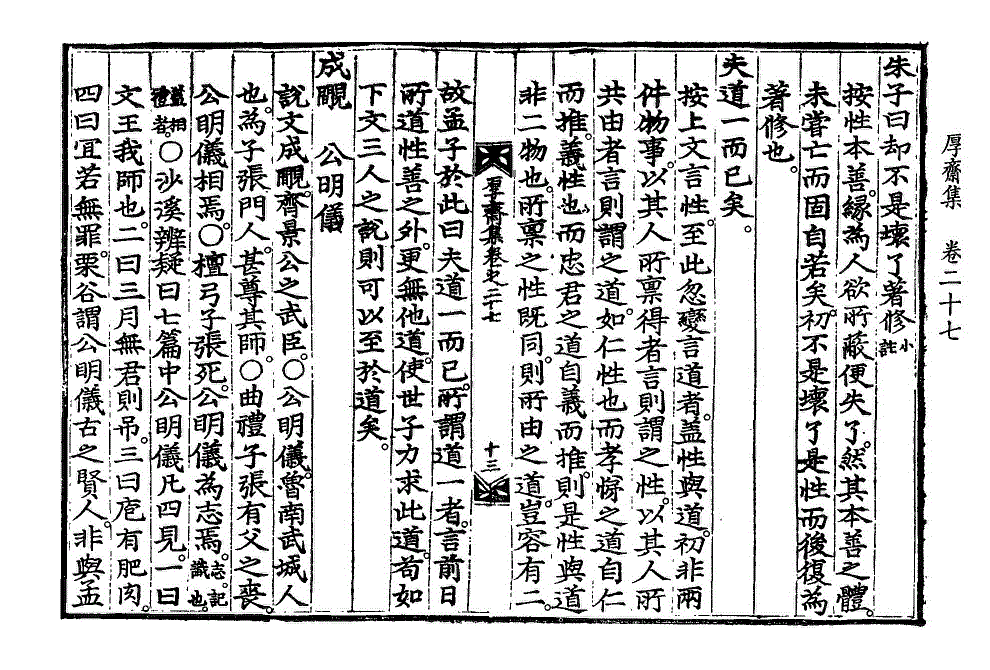 朱子曰却不是坏了著修(小注)
朱子曰却不是坏了著修(小注)按性本善。缘为人欲所蔽便失了。然其本善之体。未尝亡而固自若矣。初不是坏了是性而后复为著修也。
夫道一而已矣。
按上文言性。至此忽变言道者。盖性与道。初非两件物事。以其人所禀得者言则谓之性。以其人所共由者言则谓之道。如仁性也而孝悌之道自仁而推。义性也而忠君之道自义而推。则是性与道非二物也。所禀之性既同。则所由之道。岂容有二。故孟子于此曰夫道一而已。所谓道一者。言前日所道性善之外。更无他道。使世子力求此道。苟如下文三人之说则可以至于道矣。
成覵 公明仪
说文成覵。齐景公之武臣。○公明仪。鲁南武城人也。为子张门人。甚尊其师。○曲礼子张有父之丧。公明仪相焉。○檀弓子张死。公明仪为志焉。(志。记识也。盖相礼者。)○沙溪辨疑曰七篇中公明仪凡四见。一曰文王我师也。二曰三月无君则吊。三曰庖有肥肉。四曰宜若无罪。栗谷谓公明仪古之贤人。非与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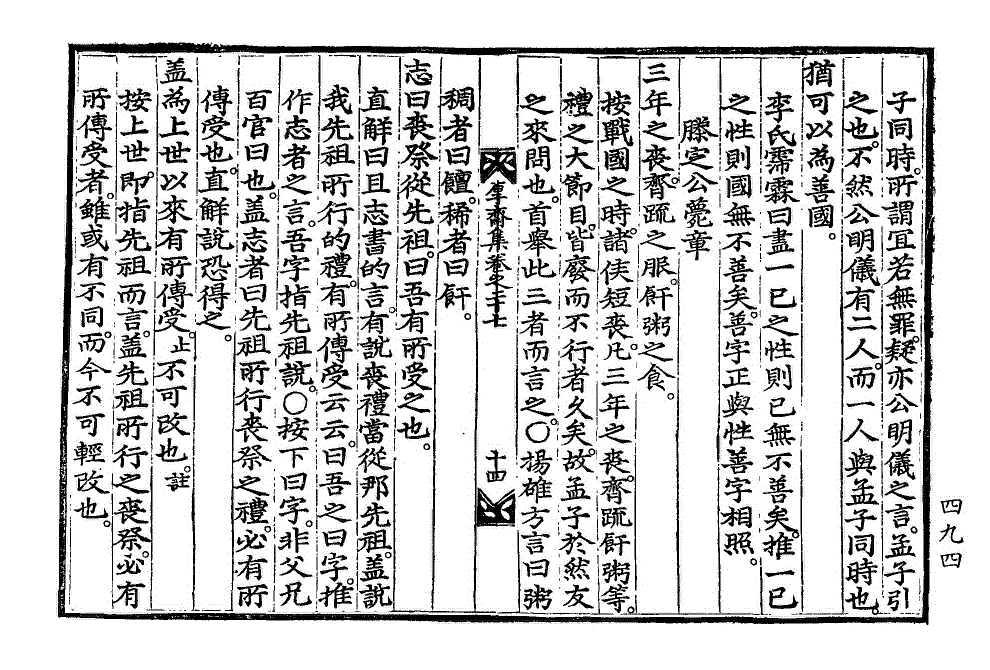 子同时。所谓宜若无罪。疑亦公明仪之言。孟子引之也。不然公明仪有二人。而一人与孟子同时也。
子同时。所谓宜若无罪。疑亦公明仪之言。孟子引之也。不然公明仪有二人。而一人与孟子同时也。犹可以为善国。
李氏霈霖曰尽一已之性则已无不善矣。推一已之性则国无不善矣。善字正与性善字相照。
滕定公薨章
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
按战国之时。诸侯短丧。凡三年之丧。齐疏饘粥等。礼之大节目。皆废而不行者久矣。故孟子于然友之来问也。首举此三者而言之。○扬雄方言曰粥稠者曰饘。稀者曰饘。
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直解曰且志书的言。有说丧礼当从那先祖。盖说我先祖所行的礼。有所传受云云。曰吾之曰字。推作志者之言。吾字指先祖说。○按下曰字。非父兄百官曰也。盖志者曰先祖所行丧祭之礼。必有所传受也。直解说恐得之。
盖为上世以来有所传受。(止)不可改也。(注)
按上世。即指先祖而言。盖先祖所行之丧祭。必有所传受者。虽或有不同。而今不可轻改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5H 页
 然志所言。本谓先王之世。(止)不谓后世失礼之甚者。(注)
然志所言。本谓先王之世。(止)不谓后世失礼之甚者。(注)按以志之本意推之。初不为此而言也。盖汎言丧祭之礼。所当从先祖而已。滕之父兄百官。引以为不行三年丧。乃是从先祖云则误矣。故集注之说如此。所谓失礼之甚者。即指不行三年丧而言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
按文公于此。乃曰吾他日未尝学问云。则其自责自悔之意。蔼然发见矣。故及闻孟子是在世子之一言。则其心自然感动。遂断然行之 而无所迟疑也。
是在世子
按上文曰亲丧固所自尽。此曰不可他求。又曰是在世子。并责之于文公之身。而不屑屑于节文之末。此所以致文公之易为感发。而亦孟子之善为喻人处也。○是在世子四字甚好。文公之感发。专在此处。盖文公闻此言而有所感悟。故便即曰是诚在我。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按此时文公新遭定公之丧。其哀苦痛疾之情。自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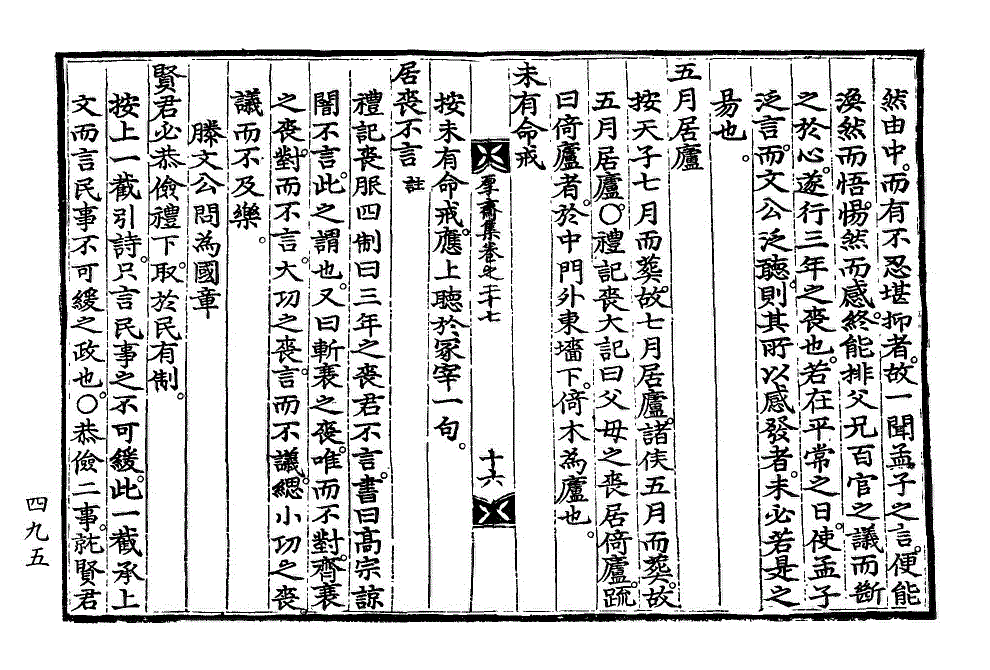 然由中。而有不忍堪抑者。故一闻孟子之言。便能涣然而悟。惕然而感。终能排父兄百官之议而断之于心。遂行三年之丧也。若在平常之日。使孟子泛言。而文公泛听。则其所以感发者。未必若是之易也。
然由中。而有不忍堪抑者。故一闻孟子之言。便能涣然而悟。惕然而感。终能排父兄百官之议而断之于心。遂行三年之丧也。若在平常之日。使孟子泛言。而文公泛听。则其所以感发者。未必若是之易也。五月居庐
按天子七月而葬。故七月居庐。诸侯五月而葬。故五月居庐。○礼记丧大记曰父母之丧居倚庐。疏曰倚庐者。于中门外东墙下。倚木为庐也。
未有命戒
按未有命戒。应上听于冢宰一句。
居丧不言(注)
礼记丧服四制曰三年之丧君不言。书曰高宗谅闇不言。此之谓也。又曰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大功之丧。言而不议。缌小功之丧。议而不及乐。
滕文公问为国章
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按上一截引诗。只言民事之不可缓。此一截承上文而言民事不可缓之政也。○恭俭二事。就贤君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6H 页
 身上言也。礼下取民有制二事。即就贤君能推恭俭而施于政者言也。○蔡氏清曰上言仁人之急于制民产。只是俭德。下复兼恭俭者。盖恭者必俭。俭者必恭。且分田制 禄二者相须。制禄即礼下之事。分田即制民产之事。故于此兼言之。
身上言也。礼下取民有制二事。即就贤君能推恭俭而施于政者言也。○蔡氏清曰上言仁人之急于制民产。只是俭德。下复兼恭俭者。盖恭者必俭。俭者必恭。且分田制 禄二者相须。制禄即礼下之事。分田即制民产之事。故于此兼言之。阳货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按为富不仁一句。应上文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一段也。为仁不富一句。应上文贤君恭俭礼下取民有制一段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止)其实皆什一。
按此段引三代所以制民产。取民有制之法。而结上文民事不可缓之意。且应贤君恭俭礼下取民有制一截。○夏后氏五十而贡。是于一夫所受五十亩之内。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其法就十亩中贡其一亩。则是即十分之一也。殷人七十而助。是于一夫所受七十亩之外。计其七亩以为公田。其法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各七十亩。以中间七十亩为公田。而就公田七十亩中。以十四亩为治田时庐舍。则所馀者五十六亩也。七八五十六。而(八家各治七亩。则恰满五十六亩之数。)八夫各治所馀公田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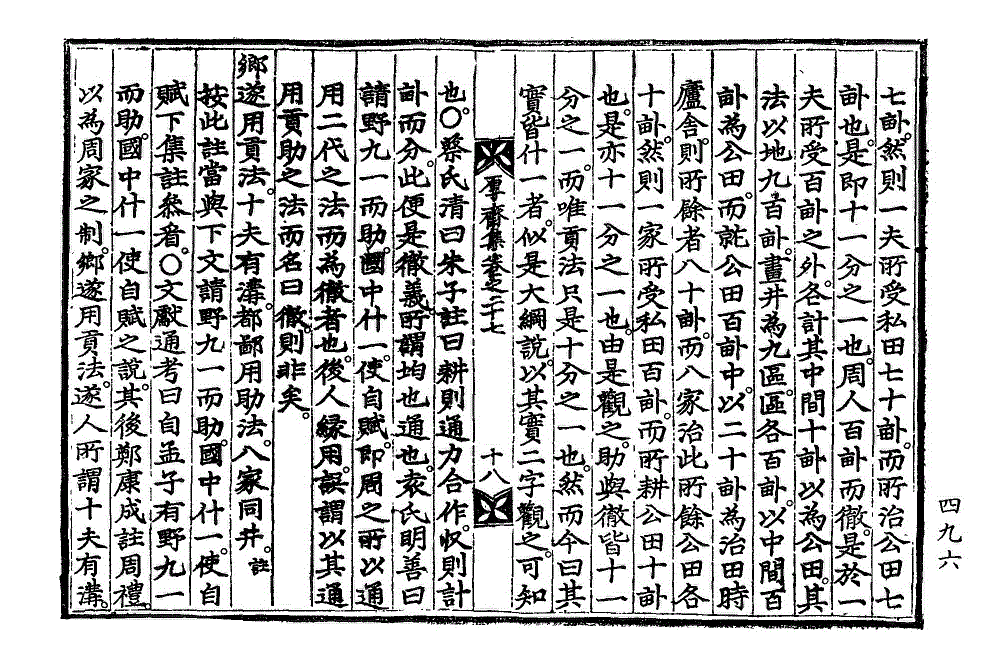 七亩。然则一夫所受私田七十亩。而所治公田七亩也。是即十一分之一也。周人百亩而彻。是于一夫所受百亩之外。各计其中间十亩以为公田。其法以地九百亩。画井为九区。区各百亩。以中间百亩为公田。而就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治田时庐舍。则所馀者八十亩。而八家治此所馀公田各十亩。然则一家所受私田百亩。而所耕公田十亩也。是亦十一分之一也。由是观之。助与彻皆十一分之一。而唯贡法只是十分之一也。然而今曰其实皆什一者。似是大纲说。以其实二字观之。可知也。○蔡氏清曰朱子注曰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而分。此便是彻义。所谓均也通也。袁氏明善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为彻者也。后人缘用。误谓以其通用贡助之法而名曰彻。则非矣。
七亩。然则一夫所受私田七十亩。而所治公田七亩也。是即十一分之一也。周人百亩而彻。是于一夫所受百亩之外。各计其中间十亩以为公田。其法以地九百亩。画井为九区。区各百亩。以中间百亩为公田。而就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治田时庐舍。则所馀者八十亩。而八家治此所馀公田各十亩。然则一家所受私田百亩。而所耕公田十亩也。是亦十一分之一也。由是观之。助与彻皆十一分之一。而唯贡法只是十分之一也。然而今曰其实皆什一者。似是大纲说。以其实二字观之。可知也。○蔡氏清曰朱子注曰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而分。此便是彻义。所谓均也通也。袁氏明善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为彻者也。后人缘用。误谓以其通用贡助之法而名曰彻。则非矣。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注)
按此注当与下文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下集注参看。○文献通考曰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后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遂人所谓十夫有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7H 页
 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 合为一法为非。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于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合。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者。特言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后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于沟。自沟而达于洫。自洫而达于浍。自浍而达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蔡氏清曰郊外都鄙之地。平原广野。可画为万夫之井。故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疆界。国中乡遂之地。包山林园麓在内。难用井田齐整分画。只截长补短计之。约田百亩则授一夫。所谓沟洫者。随地之高下而为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
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 合为一法为非。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于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合。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者。特言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后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于沟。自沟而达于洫。自洫而达于浍。自浍而达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蔡氏清曰郊外都鄙之地。平原广野。可画为万夫之井。故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疆界。国中乡遂之地。包山林园麓在内。难用井田齐整分画。只截长补短计之。约田百亩则授一夫。所谓沟洫者。随地之高下而为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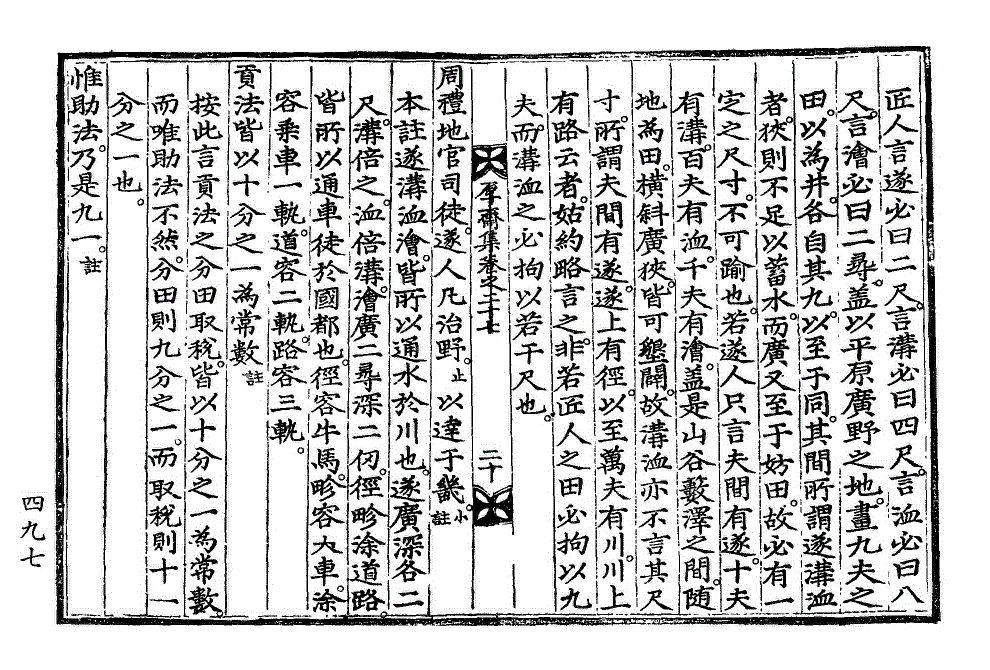 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广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间所谓遂沟洫者。狭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又至于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只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广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间所谓遂沟洫者。狭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又至于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只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周礼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止)以达于畿。(小注)
本注遂沟洫浍。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洫倍沟。浍广二寻深二仞。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于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
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注)
按此言贡法之分田取税。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而唯助法不然。分田则九分之一。而取税则十一分之一也。
惟助法。乃是九一。(注)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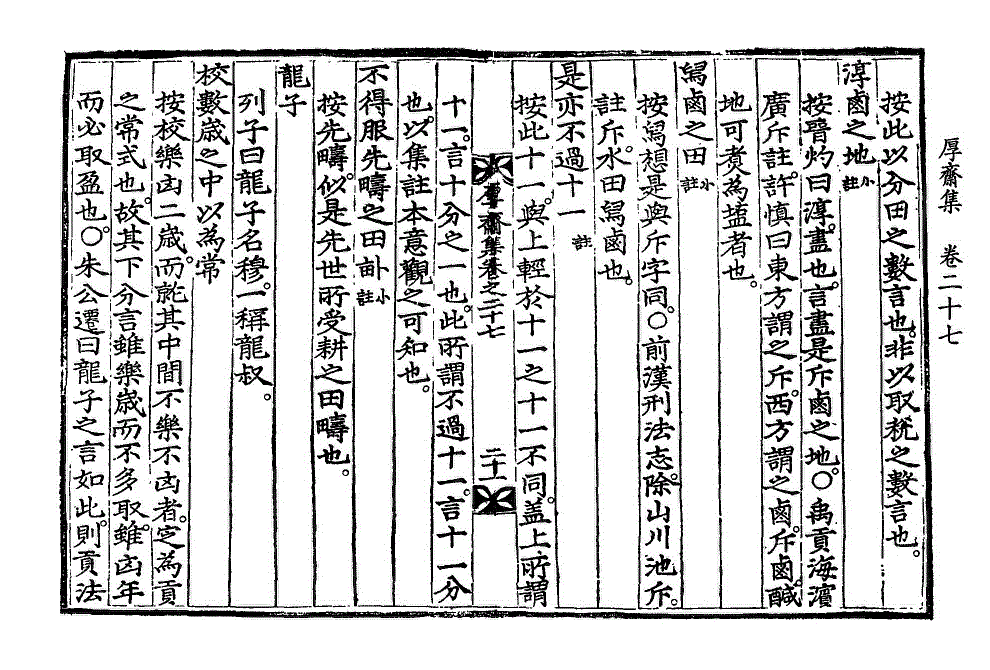 按此以分田之数言也。非以取税之数言也。
按此以分田之数言也。非以取税之数言也。淳卤之地(小注)
按晋灼曰淳。尽也。言尽是斥卤之地。○禹贡海滨广斥注。许慎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斥卤。咸地可煮为盐者也。
舄卤之田(小注)
按舄想是与斥字同。○前汉刑法志。除山川池斥。注斥。水田舄卤也。
是亦不过十一(注)
按此十一。与上轻于十一之十一不同。盖上所谓十一。言十分之一也。此所谓不过十一。言十一分也。以集注本意观之可知也。
不得服先畴之田亩(小注)
按先畴。似是先世所受耕之田畴也。
龙子
列子曰龙子名穆。一称龙叔。
校数岁之中以为常
按校乐凶二岁。而就其中间不乐不凶者。定为贡之常式也。故其下分言虽乐岁而不多取。虽凶年而必取盈也。○朱公迁曰龙子之言如此。则贡法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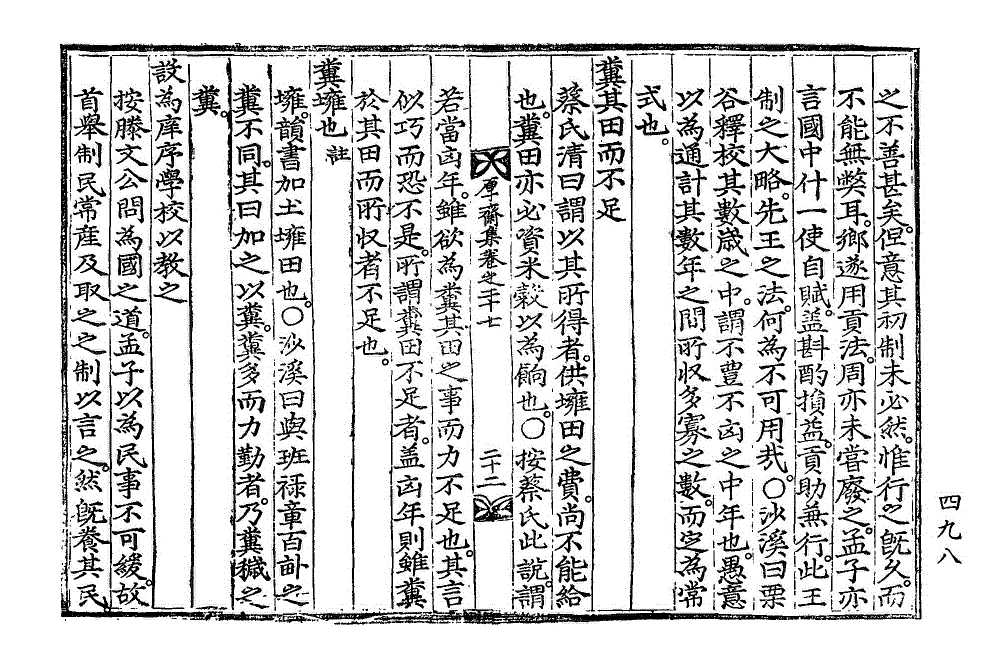 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耳。乡遂用贡法。周亦未尝废之。孟子亦言国中什一使自赋。盖斟酌损益。贡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略。先王之法。何为不可用哉。○沙溪曰栗谷释校其数岁之中。谓不丰不凶之中年也。愚意以为通计其数年之间所收多寡之数。而定为常式也。
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耳。乡遂用贡法。周亦未尝废之。孟子亦言国中什一使自赋。盖斟酌损益。贡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略。先王之法。何为不可用哉。○沙溪曰栗谷释校其数岁之中。谓不丰不凶之中年也。愚意以为通计其数年之间所收多寡之数。而定为常式也。粪其田而不足
蔡氏清曰谓以其所得者。供壅田之费。尚不能给也。粪田亦必资米谷以为饷也。○按蔡氏此说。谓若当凶年。虽欲为粪其田之事而力不足也。其言似巧而恐不是。所谓粪田不足者。盖凶年则虽粪于其田而所收者不足也。
粪壅也(注)
壅。韵书加土壅田也。○沙溪曰与班禄章百亩之粪不同。其曰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乃粪秽之粪。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按滕文公问为国之道。孟子以为民事不可缓。故首举制民常产及取之之制以言之。然既养其民。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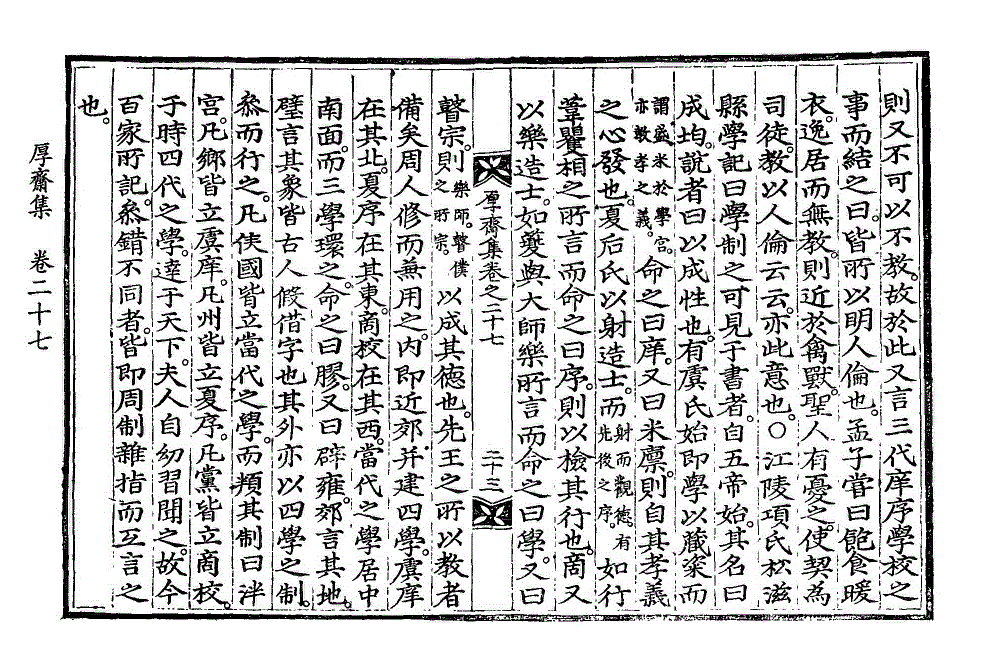 则又不可以不教。故于此又言三代庠序学校之事而结之曰。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尝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云云。亦此意也。○江陵项氏松滋县学记曰学制之可见于书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说者曰以成性也。有虞氏始即学以藏粢而(谓盛米于学宫。亦教孝之义。)命之曰庠。又曰米廪。则自其孝义之心发也。夏后氏以射造士。而(射而观德。有先后之序。)如行苇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则以检其行也。商又以乐造士。如夔与大师乐所言而命之曰学。又曰瞽宗。则(乐师。瞽仆之所宗。)以成其德也。先王之所以教者备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内即近郊并建四学。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东。商校在其西。当代之学居中南面。而三学环之。命之曰胶。又曰辟雍。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学之制。参而行之。凡侯国皆立当代之学。而頖其制曰泮宫。凡乡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党皆立商校。于时四代之学。达于天下。夫人自幼习闻之。故今百家所记。参错不同者。皆即周制杂指而互言之也。
则又不可以不教。故于此又言三代庠序学校之事而结之曰。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尝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云云。亦此意也。○江陵项氏松滋县学记曰学制之可见于书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说者曰以成性也。有虞氏始即学以藏粢而(谓盛米于学宫。亦教孝之义。)命之曰庠。又曰米廪。则自其孝义之心发也。夏后氏以射造士。而(射而观德。有先后之序。)如行苇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则以检其行也。商又以乐造士。如夔与大师乐所言而命之曰学。又曰瞽宗。则(乐师。瞽仆之所宗。)以成其德也。先王之所以教者备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内即近郊并建四学。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东。商校在其西。当代之学居中南面。而三学环之。命之曰胶。又曰辟雍。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学之制。参而行之。凡侯国皆立当代之学。而頖其制曰泮宫。凡乡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党皆立商校。于时四代之学。达于天下。夫人自幼习闻之。故今百家所记。参错不同者。皆即周制杂指而互言之也。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499L 页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按必来取法者。即指上井地学校等事而言也。滕之地方褊小。设使文公能行井地学校等事。其效不过为王者师而已。其不得自做王者可见。
亦以新子之国
按滕国虽小。苟能力行其井地之法。学校之教。一洗其旧日污习。则此便是新也。亦将日以强大。如文王之能新其命。可期也。
无君子。莫治野人。(止)莫养君子。
按无君子莫治野人。故有制禄之法。无野人莫养君子。故有分田之法。
请野九一而助。(止)使自赋。
按九一。是井地之法。什一。是贡赋之数也。○蔡氏清曰前只言治地莫善于助。至虽周亦助也。切切焉只要滕行助法。都不及贡。及答毕战则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却又兼贡。盖滕当时只是行贡法也。世禄已行者。正自将贡上之粟充世禄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则只言助法。后告毕战。不得不兼言贡助。盖授以方略形势也。
乡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井牧之法。次第是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0H 页
 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小注)
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小注)按此与首卷万乘之国千乘之家下小注所言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不同。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礼记王制曰夫圭田无征。(郑氏云夫。治也。征。税也。治圭田者不税。所以厚贤也。)注圭田者。禄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税。所以厚贤也。曰圭者洁白之义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亩。此专主祭祀。故无征。然王制言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孟子亦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无田则荐。以此知赐圭田。亦似有功德则赐圭瓒耳。○礼书云圭田。禄外之田也。馀夫。夫外之田也。禄外之田半百亩。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亩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达于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诚敬而已。后世分田。以贵贱制之。非礼意也。○按礼书说。与王制注不同。
馀夫二十五亩
礼书曰先王之民。受田虽均百亩。然其子弟之众。或食不足而力有馀。则又以馀夫任之。然馀夫之田不过二十五亩。以其家既受田百亩。又以百亩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0L 页
 予之。则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农夫之一而已。班固谓其家众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郑司农谓户计一夫一妇而赋之田。馀夫亦受此田。其说与孟子不合。○李氏霈霖曰养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治野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笃摰周详。于此见矣。
予之。则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农夫之一而已。班固谓其家众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郑司农谓户计一夫一妇而赋之田。馀夫亦受此田。其说与孟子不合。○李氏霈霖曰养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治野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笃摰周详。于此见矣。方里而井。井九百亩。
礼记王制曰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注步百为亩。是长一百步阔一步。亩百为夫。是一顷。长阔百步。夫三为屋。是三顷。阔三百步长一百步。屋三为井。则九百亩也。长阔一里。
新安陈氏曰丧礼有节文。经界之法有制度。(小注)
按集注曰当礼法废坏之后。制度节文。不可复考。此即承上丧礼经界两章六字而总言也。且制度节文上曰礼法废坏。礼即丧礼也。法即经界之法也。以此观之。所谓制度节文。似是统指丧礼井地两事而言也。盖丧礼中也有制度节文。井地中也有制度节文。今陈氏分而属之。未知其如何也。
索性坏却(小注)
索性。语录犹言白直。又犹直截。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1H 页
 有为神农之言者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章有为神农之言者
四书汇考云神农姓伊祈。名轨。又名石年。教民始为稼穑。谓之先啬。神其农业。谓之神农。○史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故因以为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亦曰厉山氏。礼记祭法(篇名)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
尽弃其学而学焉
按孟子于此。先说尽弃其学而学一段。盖若无此一段。则下文所谓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及所引子贡,曾子等语。并不照应。
滕君则诚贤君也
按陈相于此。首言诚贤君者。以滕君行井地仁政。故曰诚贤君也。次言贤者贤。即指神农之类。盖引古贤能尽神农之道者而證之也。终言恶得贤。言滕有仓廪府库而厉民自养。则前所谓诚贤君者。非实为贤君也。三贤字。各有所指。
曰冠素
礼记杂记曰鞸以素。郑注曰素。生帛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1L 页
 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
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按许行即匹夫之身。而以自织冠素。犹为害耕。况人君躬莅四海。身总万几。而与民并耕。则独不害于治乎。此不须待下文许多辨说。只此一句。可见陈相之说已败露。而亦可见其说行不得处矣。
此语八反(注)
按自孟子曰(止)曰然为一反。自许子必织布(止)衣褐为二反。自许子冠乎(止)曰冠为三反。自曰奚冠(止)冠素为四反。自曰自织(止)以粟易之为五反。自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止)害于耕为六反。自曰许子以釜甑(止)曰然为七反。自自为之(止)以粟易之为八反。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止)固不可耕且为也。
按许子以滕之仓廪府库。为厉民自养。然许子亦不免以粟易械器。则是亦为厉陶冶耶。夫人之以粟易械器者。既不为厉陶冶。而陶冶之以械器易粟者。亦不为厉农夫。则今滕君之有仓廪府库。岂独为厉民哉。不为厉陶冶。岂为厉农夫两句。并所以攻上厉民以自养之厉字也。○许子之不能耕且陶冶。正如人君之不能耕且治民。则是其所望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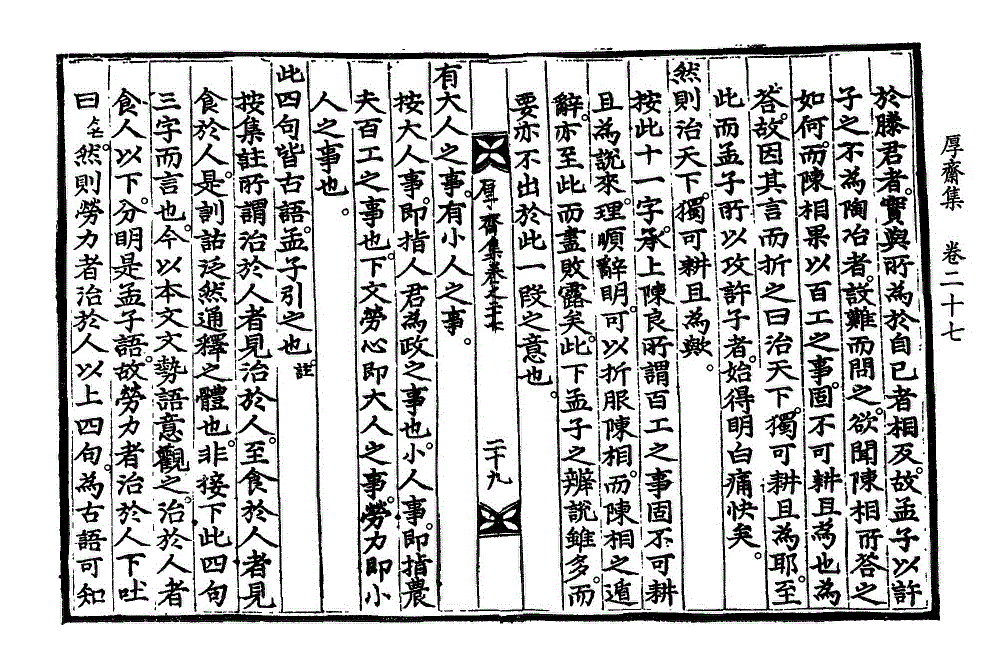 于滕君者。实与所为于自己者相反。故孟子以许子之不为陶冶者。设难而问之。欲闻陈相所答之如何。而陈相果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为答。故因其言而折之曰治天下。独可耕且为耶。至此而孟子所以攻许子者。始得明白痛快矣。
于滕君者。实与所为于自己者相反。故孟子以许子之不为陶冶者。设难而问之。欲闻陈相所答之如何。而陈相果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为答。故因其言而折之曰治天下。独可耕且为耶。至此而孟子所以攻许子者。始得明白痛快矣。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
按此十一字。承上陈良所谓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说来。理顺辞明。可以折服陈相。而陈相之遁辞。亦至此而尽败露矣。此下孟子之辨说虽多。而要亦不出于此一段之意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按大人事。即指人君为政之事也。小人事。即指农夫百工之事也。下文劳心即大人之事。劳力即小人之事也。
此四句皆古语。孟子引之也。(注)
按集注所谓治于人者见治于人。至食于人者见食于人。是训诂泛然通释之体也。非接下此四句三字而言也。今以本文文势语意观之。治于人者食人以下。分明是孟子语。故劳力者治于人下吐曰()。然则劳力者治于人以上四句。为古语可知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2L 页
 也。且通下治人者食于人为古语。则是六句非四句也。且其下天下之通义也六字。亦语势孤单。文意又不畅。○沙溪曰谚解以治于人以上作四句而为古语非是。恐以或劳心为一句。或劳力为一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一句。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为一句。以注意观之可见。○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分明是二句。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分明是二句。沙溪说未知如何也。
也。且通下治人者食于人为古语。则是六句非四句也。且其下天下之通义也六字。亦语势孤单。文意又不畅。○沙溪曰谚解以治于人以上作四句而为古语非是。恐以或劳心为一句。或劳力为一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一句。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为一句。以注意观之可见。○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分明是二句。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分明是二句。沙溪说未知如何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止)虽欲耕得乎。
按此承上文大人之事及劳心者而言也。自天下犹未平至交于中国。只是言当时中国之不可食如此。以为下文舜,禹,益敷治疏瀹之张本也。中间五谷不登四字。与下文然后中国可得而食相照应。自尧独忧之至虽欲耕得乎。方言大人劳心之事也。如尧之忧。舜之敷治。益之烈山泽。禹之疏瀹排决。过门不入。皆是大人劳心治人之事也。末端虽欲耕得乎五字。实为主意。与上文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相照应。
疏九河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3H 页
 禹贡兖州。九河既道。注曰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釜五曰胡苏六曰简洁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洁为二。○尔雅疏李巡曰徒骇者。禹疏九河。以徒众故曰徒骇。太史。禹大使徒众。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处。形如覆釜。胡苏。其水下流。故曰胡苏。胡。下也。苏。流也。简。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洁言河水多止石。治之苦洁。洁苦也。钩盘。言河水曲如钩。屈曲如盘也。鬲津。河水狭小。可鬲以为津也。○楚骚注曰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也。○按以上数说观之。凡尔雅楚骚之说。皆与集注同。惟禹贡注小异。
禹贡兖州。九河既道。注曰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釜五曰胡苏六曰简洁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洁为二。○尔雅疏李巡曰徒骇者。禹疏九河。以徒众故曰徒骇。太史。禹大使徒众。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处。形如覆釜。胡苏。其水下流。故曰胡苏。胡。下也。苏。流也。简。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洁言河水多止石。治之苦洁。洁苦也。钩盘。言河水曲如钩。屈曲如盘也。鬲津。河水狭小。可鬲以为津也。○楚骚注曰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也。○按以上数说观之。凡尔雅楚骚之说。皆与集注同。惟禹贡注小异。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
禹贡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注漯者。河之枝流也。地志曰漯水出东郡东武阳。至千乘入海。○导沇水。东流为济。注沇水。济水也。发源为沇。既东为济。地志曰济水出河东郡垣曲县王屋山。○水经注云汝水出鲁阳县之大盂山黄柏谷。由上蔡西平汝阳入淮。○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注水源发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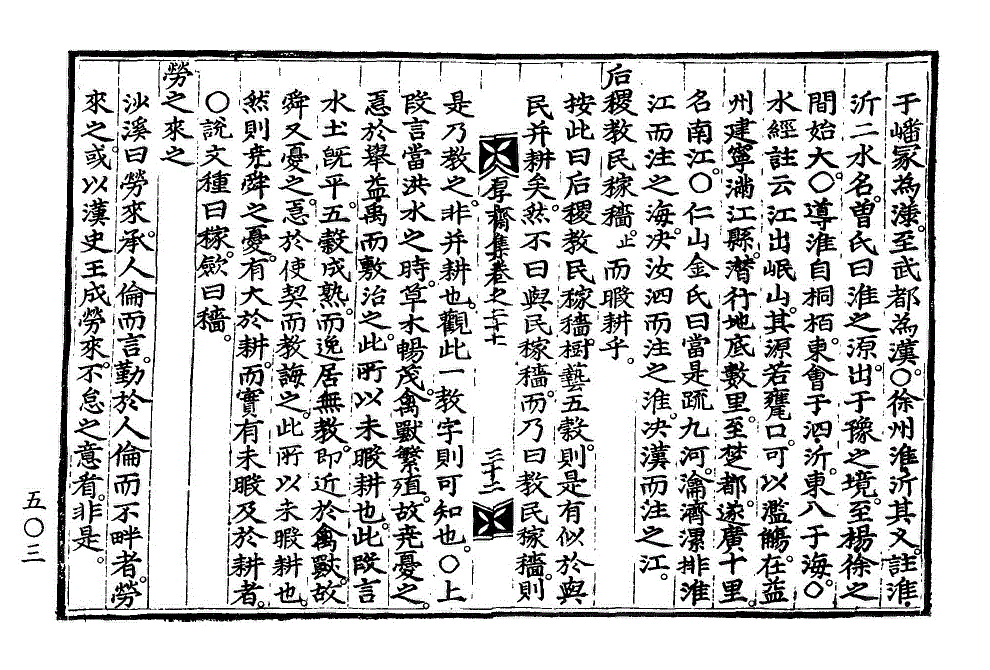 于嶓冢为漾。至武都为汉。○徐州淮,沂其又。注淮,沂二水名。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杨,徐之间始大。○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水经注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瓮口。可以滥觞。在益州建宁满江县。潜行地底数里。至楚都。遂广十里。名南江。○仁山金氏曰当是疏九河。瀹济漯排淮江而注之海。决汝泗而注之淮。决汉而注之江。
于嶓冢为漾。至武都为汉。○徐州淮,沂其又。注淮,沂二水名。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杨,徐之间始大。○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水经注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瓮口。可以滥觞。在益州建宁满江县。潜行地底数里。至楚都。遂广十里。名南江。○仁山金氏曰当是疏九河。瀹济漯排淮江而注之海。决汝泗而注之淮。决汉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止)而暇耕乎。
按此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则是有似于与民并耕矣。然不曰与民稼穑。而乃曰教民稼穑。则是乃教之。非并耕也。观此一教字则可知也。○上段言当洪水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故尧忧之。急于举益,禹而敷治之。此所以未暇耕也。此段言水土既平。五谷成熟。而逸居无教。即近于禽兽。故舜又忧之。急于使契而教诲之。此所以未暇耕也。然则尧,舜之忧。有大于耕。而实有未暇及于耕者。○说文种曰稼。敛曰穑。
劳之来之
沙溪曰劳来。承人伦而言。勤于人伦而不畔者。劳来之。或以汉史王成劳来。不怠之意看。非是。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4H 页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止)为已忧者。农夫也。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止)为已忧者。农夫也。按此段。又承上文尧独忧之及圣人有忧之及圣人之忧民如此而言也。盖尧舜之所忧。大人劳心之事。农夫之所忧。小人劳力之事也。今许子欲以百亩之忧。为万乘之忧。不亦误乎。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止)亦不用于耕耳。
按此段承上文而特拈出尧舜二圣人。言尧舜之为君。若是其盛且大也。其于治民。宜无所不用其心。而然亦不与民并耕而食也。若如许行之言。以与民并耕。谓之闻道。则以尧舜无所不用心于治天下者。岂不为之哉。盖言此深折许行与民并耕之说也。
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止)师死而遂倍之。
按以吾闻二字观之。用夏变夷。必是古语也。○此以上。只是深辟许行之道。自此以下。方承上文尽弃其学而学之一段。只责陈相倍师之罪也。下至鲁颂。皆一意也。
失声然后归。
赵氏旧注曰失声。悲不能成声也。
反筑室于场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4L 页
 孙氏正义曰按史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去城一里。冢营百亩。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冢前以缶甓为祠坛。方六尺。○四书汇考云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名曰孔里。
孙氏正义曰按史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去城一里。冢营百亩。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冢前以缶甓为祠坛。方六尺。○四书汇考云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名曰孔里。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史记列传。有子少孔子四十三岁。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共立为师。师事之。○家语有若强识好古。习礼乐。孔子没。弟子以有若言貌气像相似。共立为师。○朱子曰柳宗元以为孔子之没。诸子尝以有子似夫子而师之。后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当时既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有子曷尝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按以朱子说观之。史记所谓师事之。家语所谓共立为师者。误矣。
盖其言行气像。有似之者。(注)
按此集注云云。必是本于家语言貌气像相似之说而言之也。
今也南蛮鴃舌之人。(止)亦异于曾子矣。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5H 页
 按今也二字。对上文昔者二字而言也。上文既承上师死遂倍之说。而引子贡,曾子之事。以明圣门弟子不背师之意。于此结之曰亦异于曾子矣。所以深责陈相也。
按今也二字。对上文昔者二字而言也。上文既承上师死遂倍之说。而引子贡,曾子之事。以明圣门弟子不背师之意。于此结之曰亦异于曾子矣。所以深责陈相也。鲁颂曰戎狄是膺。(止)亦为不善变矣。
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是善变也。今陈相初学于北学中国之陈良。而卒乃受变于南蛮鴃舌之许行。则是即不善变也。此不善变三字。不可但就戎狄是膺一段上看。自上文下乔木入幽谷一截串贯看来。则文势连属。意味方好。○盖自吾闻用夏变夷。仍说到南蛮鴃舌。而乃结之曰亦异于曾子矣。自吾闻出于幽谷。仍说到戎狄是膺。而乃结之曰亦为不善变矣。看此两个吾闻二字。则其为两截。意自分晓。
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注)
按下好辩章亦引此诗而结之曰。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亦以周公言之。其意与此同。
从许子之道。(止)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按许行之道。无他奇异可以耸动人者。只曰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云云。其言不成事理。不成说话。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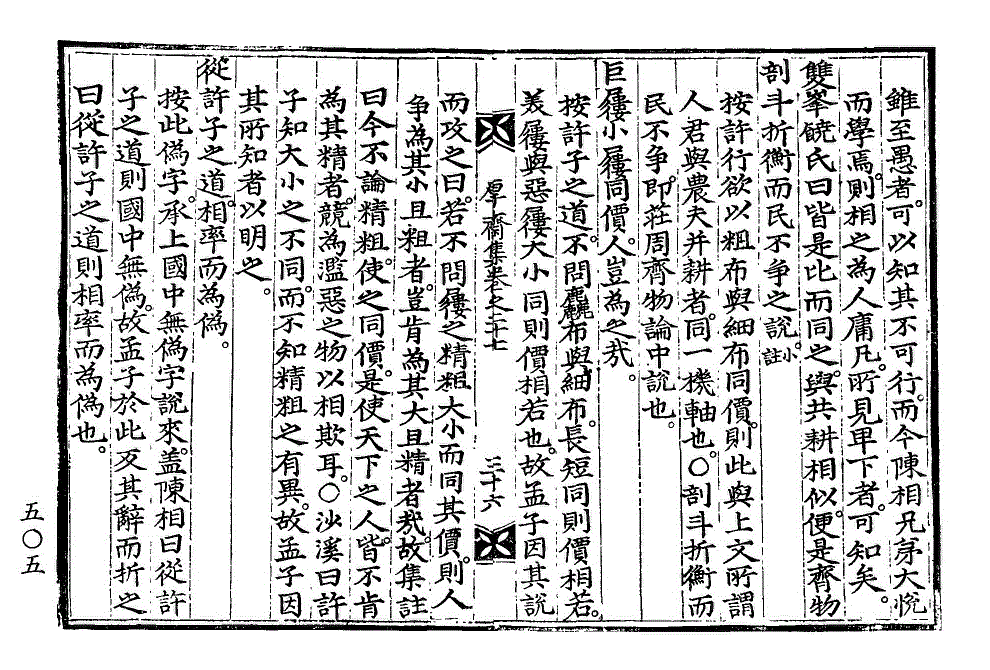 虽至愚者。可以知其不可行。而今陈相兄弟大悦而学焉。则相之为人庸凡。所见卑下者。可知矣。
虽至愚者。可以知其不可行。而今陈相兄弟大悦而学焉。则相之为人庸凡。所见卑下者。可知矣。双峰饶氏曰皆是比而同之。与共耕相似。便是齐物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之说。(小注)
按许行欲以粗布与细布同价。则此与上文所谓人君与农夫并耕者。同一机轴也。○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即庄周齐物论中说也。
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
按许子之道。不问粗布与细布。长短同则价相若。美屦与恶屦大小同则价相若也。故孟子因其说而攻之曰。若不问屦之精粗大小而同其价。则人争为其小且粗者。岂肯为其大且精者哉。故集注曰今不论精粗。使之同价。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为其精者。竞为滥恶之物以相欺耳。○沙溪曰许子知大小之不同。而不知精粗之有异。故孟子因其所知者以明之。
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
按此伪字。承上国中无伪字说来。盖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国中无伪。故孟子于此反其辞而折之曰从许子之道则相率而为伪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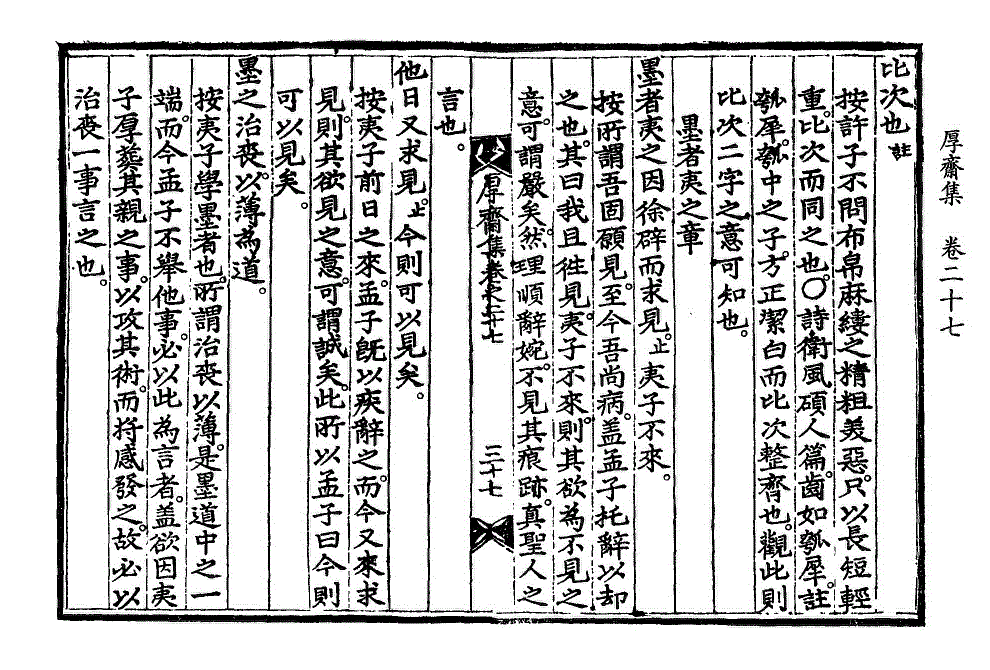 比次也(注)
比次也(注)按许子不问布帛麻缕之精粗美恶。只以长短轻重。比次而同之也。○诗卫风硕人篇。齿如瓠犀。注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洁白而比次整齐也。观此则比次二字之意可知也。
墨者夷之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止)夷子不来。
按所谓吾固愿见。至今吾尚病。盖孟子托辞以却之也。其曰我且往见。夷子不来。则其欲为不见之意。可谓严矣。然理顺辞婉。不见其痕迹。真圣人之言也。
他日又求见。(止)今则可以见矣。
按夷子前日之来。孟子既以疾辞之。而今又来求见。则其欲见之意。可谓诚矣。此所以孟子曰今则可以见矣。
墨之治丧。以薄为道。
按夷子学墨者也。所谓治丧以薄。是墨道中之一端。而今孟子不举他事。必以此为言者。盖欲因夷子厚葬其亲之事。以攻其术。而将感发之。故必以治丧一事言之也。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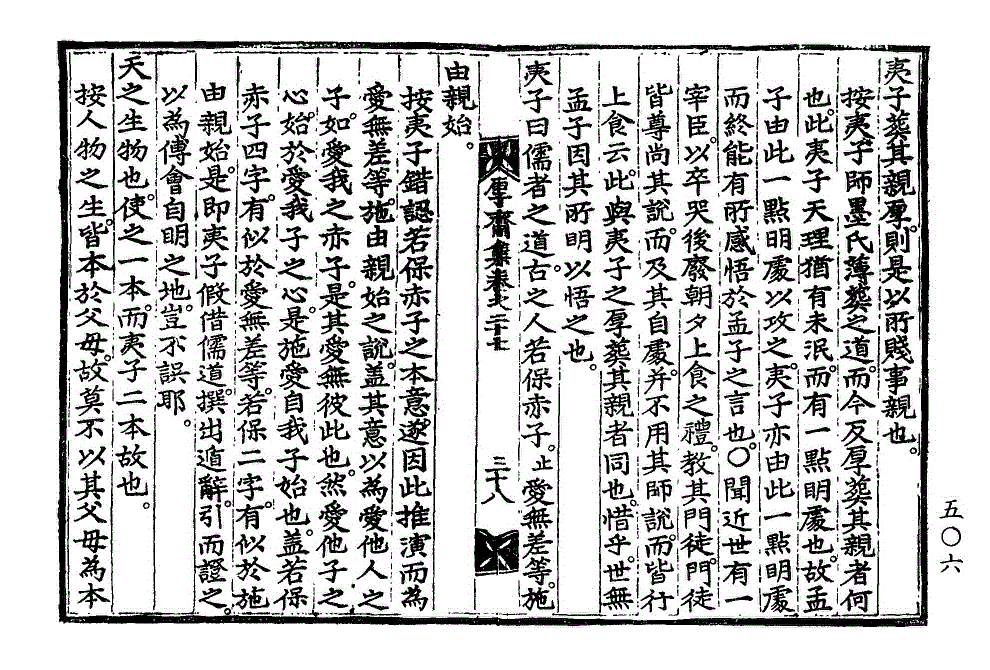 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按夷子师墨氏薄葬之道。而今反厚葬其亲者何也。此夷子天理犹有未泯。而有一点明处也。故孟子由此一点明处以攻之。夷子亦由此一点明处而终能有所感悟于孟子之言也。○闻近世有一宰臣。以卒哭后废朝夕上食之礼。教其门徒。门徒皆尊尚其说。而及其自处。并不用其师说。而皆行上食云。此与夷子之厚葬其亲者同也。惜乎。世无孟子因其所明以悟之也。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止)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按夷子错认若保赤子之本意。遂因此推演而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之说。盖其意以为爱他人之子。如爱我之赤子。是其爱无彼此也。然爱他子之心。始于爱我子之心。是施爱自我子始也。盖若保赤子四字。有似于爱无差等。若保二字。有似于施由亲始。是即夷子假借儒道。撰出遁辞。引而證之。以为传会自明之地。岂不误耶。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按人物之生。皆本于父母。故莫不以其父母为本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7H 页
 是所谓一本也。如木之枝叶虽多。而皆本于一根也。惟墨氏兼爱而爱无差等。则是非但亲其亲。而又亲路人之亲。即所谓二本也。其与天之生物而使之一本者相反。
是所谓一本也。如木之枝叶虽多。而皆本于一根也。惟墨氏兼爱而爱无差等。则是非但亲其亲。而又亲路人之亲。即所谓二本也。其与天之生物而使之一本者相反。援儒而入于墨(注)
按若保赤子。是儒者之说。而今夷子引之。欲同于墨之兼爱。故曰援儒而入于墨。
推墨而附于儒(注)
按爱无差等。是墨道也。施由亲始。似儒道也。今夷子以爱无差等之墨道。欲浑于施由亲始之似儒道者。故曰推墨而附于儒。
庆源辅氏曰此仁义所以相为用也。(小注)
按墨道只欲为仁。而未有义以裁制之也。是仁义不相为用也。
若天使之(注)
按所谓天使者。即莫之为而为也。天使与自然。是一意也。
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
按此段。即承上文墨者薄葬之道而言。以警夷子。而其所云云。哀痛迫切。有若针刺。足以感动人。故
厚斋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第 507L 页
 夷子闻之。便能惕然感悟也。
夷子闻之。便能惕然感悟也。盖归反蔂梩而掩之。
按其颡有泚及蔂梩掩之者何也。盖以其一本故也。若爱无差等则(二本)其视之当与路人无异矣。岂有此颡泚蔂梩之事哉。○退溪曰归。归其家也。反。覆也。言盛土于器。覆而泻之于地也。○沙溪曰归。疑复归尸处也。
夷子怃然为间
按夷子闻孟子之言。而能翻然感悟。虽缘天理自然发动故如此。想夷子亦非庸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