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鹤庵集卷之四 第 x 页
鹤庵集卷之四
华阳闻见录
华阳闻见录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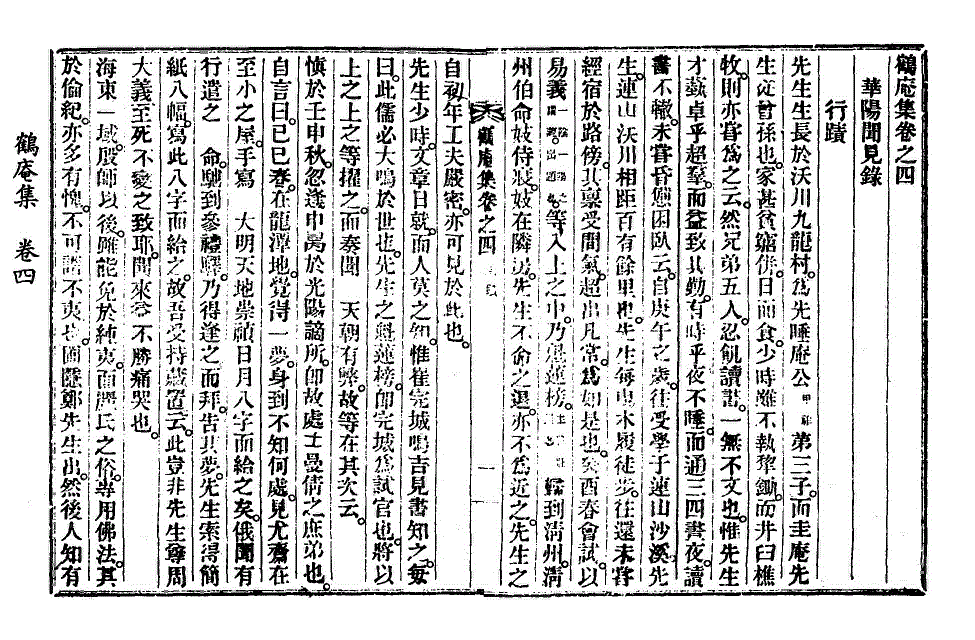 行迹
行迹先生生长于沃川九龙村。为先睡庵公(甲祚)第三子。而圭庵先生从曾孙也。家甚贫穷并。日而食。少时虽不执犁锄。而井臼樵牧。则亦尝为之云。然兄弟五人。忍饥读书。一无不文也。惟先生才蓻卓乎超群。而益致其勤。有时乎夜不睡。而通三四昼夜。读书不辙。未尝昏惫困卧云。自庚午之岁。往受学于连山沙溪先生。连山沃川相距百有馀里也。先生每曳木履徒步。往还未尝经宿于路傍。其禀受间气。超出凡常。为如是也。癸酉春会试。以易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出题也。)等入上之中。乃魁莲榜。(生员壮员也)归到清州。清州伯命妓侍寝。妓在邻房。先生不命之退。亦不为近之。先生之自初年工夫严密。亦可见于此也。
先生少时。文章日就。而人莫之知。惟崔完城鸣吉见书知之。每曰。此儒必大鸣于世也。先生之魁莲榜。即完城为试官也。将以上之上之等擢之。而奏闻 天朝有弊。故等在其次云。
慎于壬申秋。忽逢中申于光阳谪所。即故处士曼倩之庶弟也。自言曰。己巳春。在龙潭地。觉得一梦。身到不知何处。见尤斋在至小之屋。手写 大明天地崇祯日月八字而给之矣。俄闻有行遣之 命。驰到参礼驿。乃得逢之而拜。告其梦。先生索得简纸八幅。写此八字而给之。故吾受持藏置云。此岂非先生尊周大义至死不变之致耶。闻来益不胜痛哭也。
海东一域。殷师以后。虽能免于纯夷。而丽氏之俗。专用佛法。其于伦纪。亦多有愧。不可谓不夷也。圃隐郑先生出。然后人知有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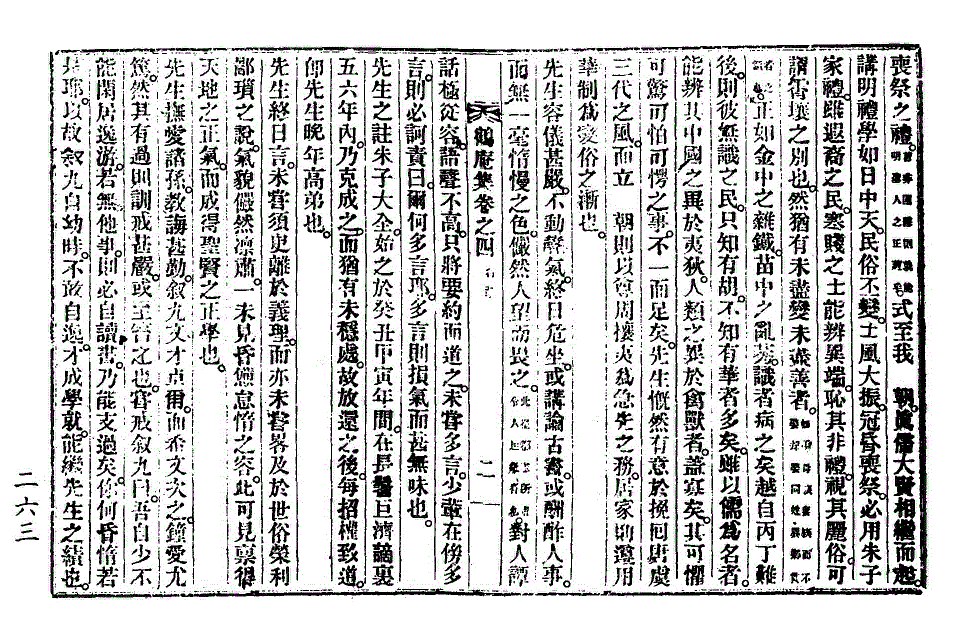 丧祭之礼。(若非圃隐则孰能明圣人之正道乎。)式至我 朝。真儒大贤相继而起。讲明礼学如日中天。民俗丕变。士风大掁。冠昏丧祭。必用朱子家礼。虽遐裔之民。寒贱之士能辨异端。耻其非礼。视其丽俗。可谓霄壤之别也。然犹有未尽变未尽善者。(如重母族妻族而不娶却娶同姓异乡贯者之类也。)正如金中之杂铁。苗中之乱莠。识者病之矣。越自丙丁难后。则彼无识之民。只知有胡。不知有华者多矣。虽以儒为名者。能辨其中国之异于夷狄。人类之异于禽兽者。盖寡矣。其可惧可惊可怕可愕之事。不一而足矣。先生慨然有意于挽回唐虞三代之风。而立 朝则以尊周攘夷为急先之务。居家则遵用华制为变俗之渐也。
丧祭之礼。(若非圃隐则孰能明圣人之正道乎。)式至我 朝。真儒大贤相继而起。讲明礼学如日中天。民俗丕变。士风大掁。冠昏丧祭。必用朱子家礼。虽遐裔之民。寒贱之士能辨异端。耻其非礼。视其丽俗。可谓霄壤之别也。然犹有未尽变未尽善者。(如重母族妻族而不娶却娶同姓异乡贯者之类也。)正如金中之杂铁。苗中之乱莠。识者病之矣。越自丙丁难后。则彼无识之民。只知有胡。不知有华者多矣。虽以儒为名者。能辨其中国之异于夷狄。人类之异于禽兽者。盖寡矣。其可惧可惊可怕可愕之事。不一而足矣。先生慨然有意于挽回唐虞三代之风。而立 朝则以尊周攘夷为急先之务。居家则遵用华制为变俗之渐也。先生容仪甚严。不动声气。终日危坐。或讲论古书。或酬酢人事。而无一毫惰慢之色。俨然人望而畏之。(此崔都宪所谓令人起敬者也。)对人谭话极从容。语声不高。只将要约而道之。未尝多言。少辈在傍多言。则必诃责曰。尔何多言耶。多言则损气而甚无味也。
先生之注朱子大全。始之于癸丑甲寅年间。在长鬐巨济谪里五六年内。乃克成之。而犹有未稳处。故放还之后。每招权致道。即先生晚年高弟也。
先生终日言。未尝须臾离于义理。而亦未尝略及于世俗荣利鄙琐之说。气貌俨然凛肃。一未见昏惫怠惰之容。此可见禀得天地之正气。而成得圣贤之正学也。
先生抚爱诸孙。教诲甚勤。叙九文才卓尔。而希文次之。钟爱尤笃。然其有过则训戒甚严。或至笞之也。尝戒叙九曰。吾自少不能闲居逸游。若无他事。则必自读书。乃能支过矣。你何昏惰若是耶。以故叙九自幼时。不敢自逸。才成学就。能继先生之绩也。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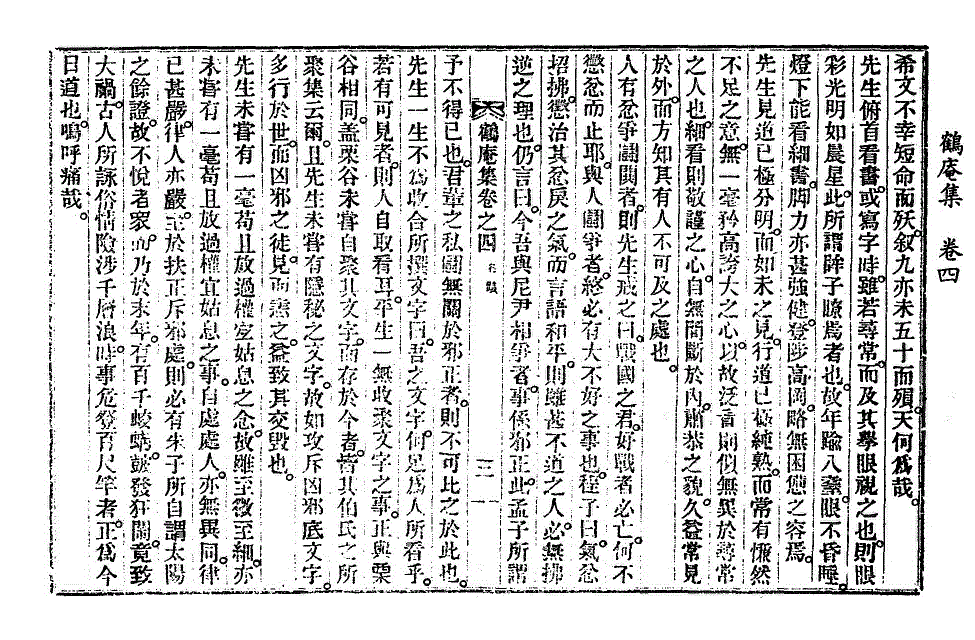 希文不幸短命而夭。叙九亦未五十而殒。天何为哉。
希文不幸短命而夭。叙九亦未五十而殒。天何为哉。先生俯首看书。或写字时。虽若寻常。而及其举眼视之也。则眼彩光明如晨星。此所谓眸子瞭焉者也。故年踰八耋。眼不昏睡。灯下能看细书。脚力亦甚强健。登陟高冈。略无困惫之容焉。
先生见道已极分明。而如未之见。行道已极纯熟。而常有慊然不足之意。无一毫矜高誇大之心。以故泛看则似无异于寻常之人也。细看则敬谨之心。自无间断于内。肃恭之貌。久益常见于外。而方知其有人不可及之处也。
人有忿争斗鬨者。则先生戒之曰。战国之君。好战者必亡。何不惩忿而止耶。与人斗争者。终必有大不好之事也。程子曰。气忿招拂。惩治其忿戾之气。而言语和平。则虽甚不道之人。必无拂逆之理也。仍言曰。今吾与尼尹相争者。事系邪正。此孟子所谓予不得已也。君辈之私斗无关于邪正者。则不可比之于此也。先生一生不为收合所撰文字曰。吾之文字。何足为人所看乎。若有可见者。则人自取看耳。平生一无收聚文字之事。正与栗谷相同。盖栗谷未尝自聚其文字。而存于今者。皆其伯氏之所聚集云尔。且先生未尝有隐秘之文字。故如攻斥凶邪底文字。多行于世。而凶邪之徒。见而恚之。益致其交毁也。
先生未尝有一毫苟且放过权宜姑息之念。故虽至微至细。亦未尝有一毫苟且放过权宜姑息之事。自处处人。亦无异同。律己甚严。律人亦严。至于扶正斥邪处。则必有朱子所自谓太阳之馀證。故不悦者众。而乃于末年。有百千蛟蜹。鼓发狂闹。竟致大祸。古人所咏俗情险涉千层浪。时事危登百尺竿者。正为今日道也。呜呼痛哉。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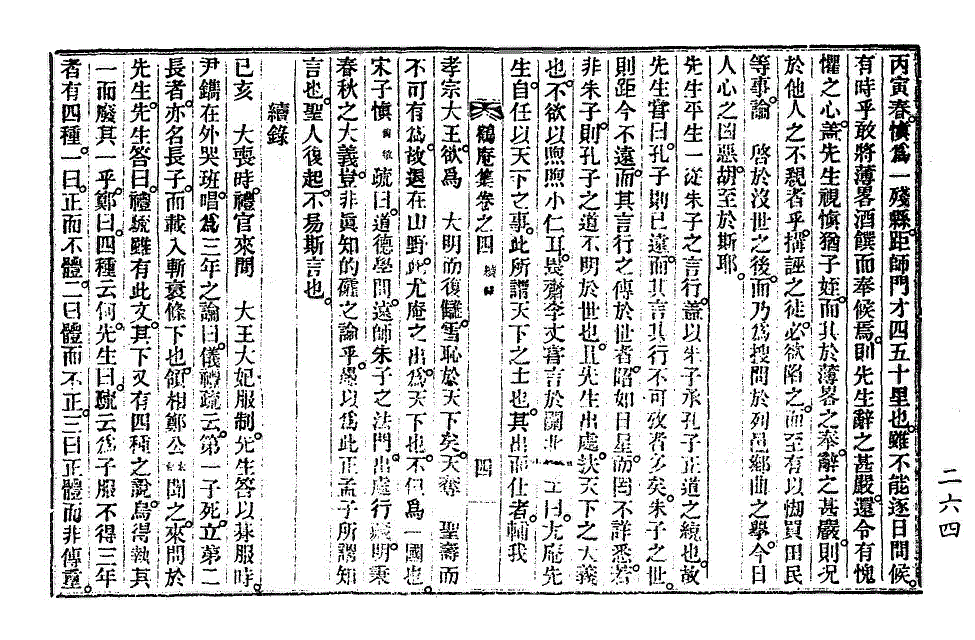 丙寅春。慎为一残县。距师门才四五十里也。虽不能逐日问候。有时乎敢将薄略酒馔而奉候焉。则先生辞之甚严。还令有愧惧之心。盖先生视慎犹子侄。而其于薄略之奉。辞之甚严。则况于他人之不亲者乎。搆诬之徒。必欲陷之。而至有以怯买田民等事。论 启于没世之后。而乃为搜问于列邑乡曲之举。今日人心之凶恶。胡至于斯耶。
丙寅春。慎为一残县。距师门才四五十里也。虽不能逐日问候。有时乎敢将薄略酒馔而奉候焉。则先生辞之甚严。还令有愧惧之心。盖先生视慎犹子侄。而其于薄略之奉。辞之甚严。则况于他人之不亲者乎。搆诬之徒。必欲陷之。而至有以怯买田民等事。论 启于没世之后。而乃为搜问于列邑乡曲之举。今日人心之凶恶。胡至于斯耶。先生平生一从朱子之言行。盖以朱子承孔子正道之统也。故先生尝曰。孔子则已远。而其言其行不可考者多矣。朱子之世。则距今不远。而其言行之传于世者。昭如日星。而罔不详悉。若非朱子。则孔子之道不明于世也。且先生出处。扶天下之大义也。不欲以煦煦小仁耳。畏斋李丈尝言于关北儒士曰。尤庵先生。自任以天下之事。此所谓天下之士也。其出而仕者。辅我 孝宗大王。欲为 大明而复雠。雪耻于天下矣。天夺 圣寿而不可有为。故退在山野。此尤庵之出。为天下也。不俱为一国也。宋子慎(尚敏)疏曰。道德学问。远师朱子之法门。出处行藏。明秉春秋之大义。岂非真知的确之论乎。愚以为此正孟子所谓知言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也。
续录
己亥 大丧时。礼官来间 大王大妃服制。先生答以期服时。尹镌在外哭班。唱为三年之论曰。仪礼疏云。第一子死。立第一长者。亦名长子。而载入斩衰条下也。领相郑公(太初)闻之。来问于先生。先生答曰。礼疏虽有此文。其下又有四种之说。乌得执其一而废其一乎。郑曰。四种云何。先生曰。疏云为子服不得三年者有四种。一曰。正而不体。二曰体而不正。三曰正体而非传重。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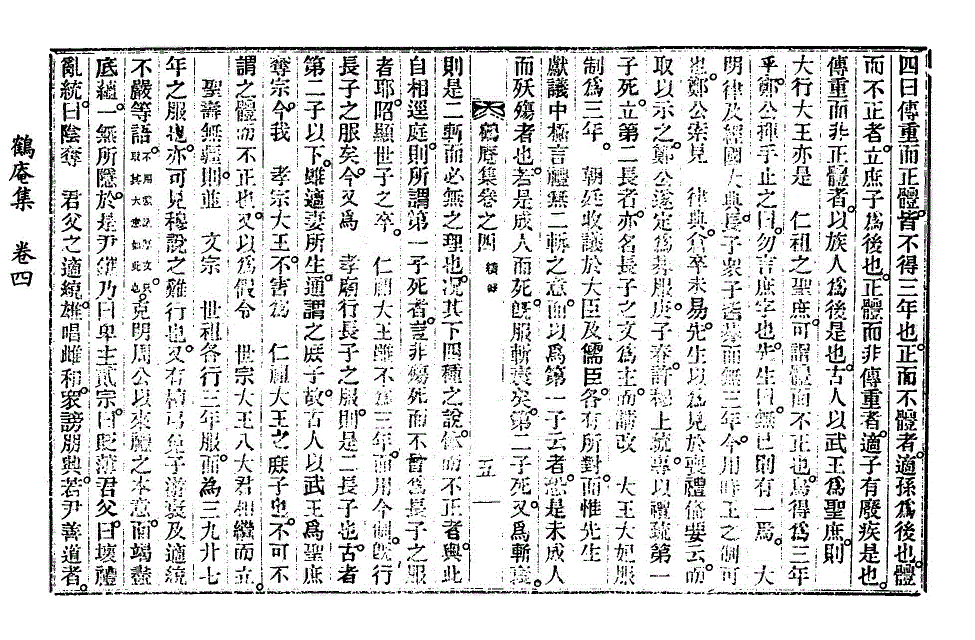 四曰传重而正体。皆不得三年也。正而不体者。适孙为后也。体而不正者。立庶子为后也。正体而非传重者。适子有废疾是也。传重而非正体者。以族人为后是也。古人以武王为圣庶。则 大行大王亦是 仁祖之圣庶。可谓体而不正也。乌得为三年乎。郑公挥手止之曰。勿言庶字也。先生曰。无已则有一焉。 大明律及经国大典。长子众子皆期而无三年。今用时王之制可也。郑公索见 律典。仓卒未易。先生以为见于丧礼备要云。而取以示之。郑公遂定为期服。庚子春。许穆上疏。专以礼疏第一子死。立第二长者。亦名长子之文为主。而请改 大王大妃服制为三年。 朝廷收议于大臣及儒臣。各有所对。而惟先生 献议中极言礼无二斩之意。而以为第一子云者。恐是未成人而夭殇者也。若是成人而死。既服斩衰矣。第二子死。又为斩衰。则是二斩而必无之理也。况其下四种之说。体而不正者。与此自相径庭。则所谓第一子死者。岂非殇死而不曾为长子之服者耶。昭显世子之卒。 仁祖大王虽不为三年。而用今制。既行长子之服矣。今又为 孝庙行长子之服。则是二长子也。古者第二子以下。虽适妻所生。通谓之庶子。故人以武王为圣庶夺宗。今我 孝宗大王。不害为 仁祖大王之庶子也。不可不谓之体而不正也。又以为假令 世宗大王八大君相继而立。 圣寿无疆。则并 文宗 世祖各行三年服。而为三九廿七年之服也。亦可见穆说之难行也。又有檀弓免子游衰及适统不严等语。(不用献议厚文。只取其大意如此也。)克明周公以来礼之本意。而竭尽底蕴。一无所隐。于是尹镌乃曰卑主贰宗。曰贬薄君父。曰坏礼乱统。曰阴夺 君父之适统。雄唱雌和。众谤朋兴。若尹善道者。
四曰传重而正体。皆不得三年也。正而不体者。适孙为后也。体而不正者。立庶子为后也。正体而非传重者。适子有废疾是也。传重而非正体者。以族人为后是也。古人以武王为圣庶。则 大行大王亦是 仁祖之圣庶。可谓体而不正也。乌得为三年乎。郑公挥手止之曰。勿言庶字也。先生曰。无已则有一焉。 大明律及经国大典。长子众子皆期而无三年。今用时王之制可也。郑公索见 律典。仓卒未易。先生以为见于丧礼备要云。而取以示之。郑公遂定为期服。庚子春。许穆上疏。专以礼疏第一子死。立第二长者。亦名长子之文为主。而请改 大王大妃服制为三年。 朝廷收议于大臣及儒臣。各有所对。而惟先生 献议中极言礼无二斩之意。而以为第一子云者。恐是未成人而夭殇者也。若是成人而死。既服斩衰矣。第二子死。又为斩衰。则是二斩而必无之理也。况其下四种之说。体而不正者。与此自相径庭。则所谓第一子死者。岂非殇死而不曾为长子之服者耶。昭显世子之卒。 仁祖大王虽不为三年。而用今制。既行长子之服矣。今又为 孝庙行长子之服。则是二长子也。古者第二子以下。虽适妻所生。通谓之庶子。故人以武王为圣庶夺宗。今我 孝宗大王。不害为 仁祖大王之庶子也。不可不谓之体而不正也。又以为假令 世宗大王八大君相继而立。 圣寿无疆。则并 文宗 世祖各行三年服。而为三九廿七年之服也。亦可见穆说之难行也。又有檀弓免子游衰及适统不严等语。(不用献议厚文。只取其大意如此也。)克明周公以来礼之本意。而竭尽底蕴。一无所隐。于是尹镌乃曰卑主贰宗。曰贬薄君父。曰坏礼乱统。曰阴夺 君父之适统。雄唱雌和。众谤朋兴。若尹善道者。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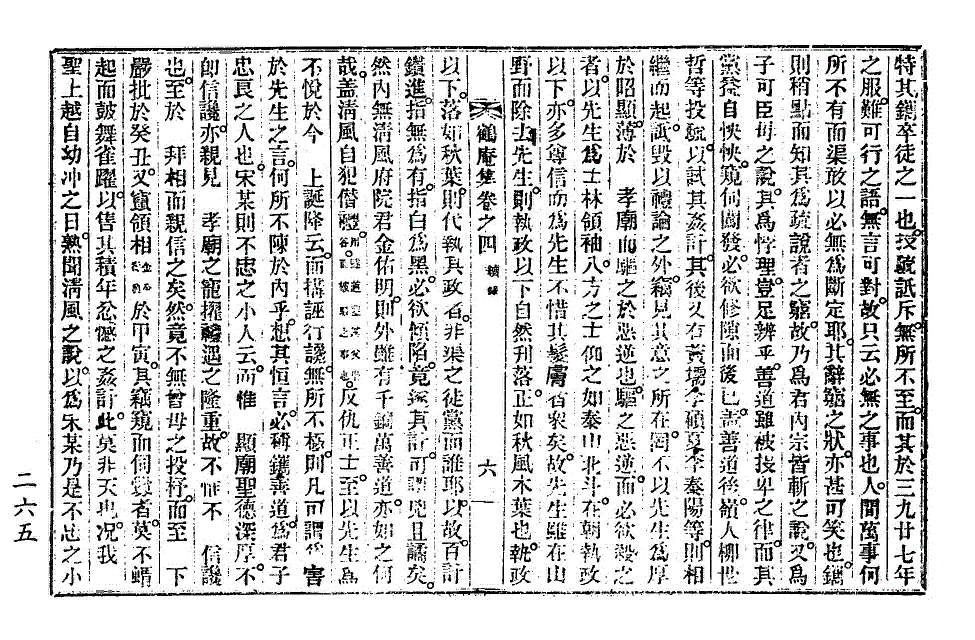 特其镌卒徒之一也。投疏诋斥。无所不至。而其于三九廿七年之服。难可行之语。无言可对。故只云必无之事也。人间万事何所不有而渠敢以必无为断定耶。其辞穷之状。亦甚可笑也。镌则稍点而知其为疏说者之穷。故乃为君内宗皆斩之说。又为子可臣母之说。其为悖理。岂足辨乎。善道虽被投卑之律。而其党益自怏怏。窥伺闯发。必欲修隙而后已。盖善道后。岭人柳世哲等投疏。以试其奸计。其后又有黄壖,李硕夏,李泰阳等。则相继而起。诋毁以礼论之外。窃见其意之所在。罔不以先生为厚于昭显。薄于 孝庙而驱之于恶逆也。驱之恶逆。而必欲杀之者。以先生为士林领袖。八方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在朝执政以下。亦多尊信而为先生不惜其发肤者众矣。故先生虽在山野而除去先生。则执政以下自然刊落。正如秋风木叶也。执政以下。落如秋叶。则代执其政者。非渠之徒党而谁耶。以故。百计钻进。指无为有。指白为黑。必欲倾陷。竟遂其计。可谓凶且谲矣。然内无清风府院君金佑明。则外虽有千镌万善道。亦如之何哉。盖清风自犯僭礼。用隧道葬其父僭(一作潜)谷。而被驳之事也。 反仇正士。至以先生为不悦于今 上诞降云。而搆诬行谗。无所不极。则凡可谓为害于先生之言。何所不陈于内乎。想其恒言。必称镌,善道。为君子忠良之人也。宋某则不忠之小人云。而惟 显庙圣德深厚。不即信谗。亦亲见 孝庙之宠擢礼遇之隆重。故不惟不 信谗也。至于 拜相而亲信之矣。然竟不无曾母之投杼。而至 下严批于癸丑。又窜领相(金公寿兴)于甲寅。其窃窥而伺衅者。莫不猬起而鼓舞雀跃。以售其积年忿憾之奸计。此莫非天也。况我 圣上越自幼冲之日。熟闻清风之说。以为宋某乃是不忠之小
特其镌卒徒之一也。投疏诋斥。无所不至。而其于三九廿七年之服。难可行之语。无言可对。故只云必无之事也。人间万事何所不有而渠敢以必无为断定耶。其辞穷之状。亦甚可笑也。镌则稍点而知其为疏说者之穷。故乃为君内宗皆斩之说。又为子可臣母之说。其为悖理。岂足辨乎。善道虽被投卑之律。而其党益自怏怏。窥伺闯发。必欲修隙而后已。盖善道后。岭人柳世哲等投疏。以试其奸计。其后又有黄壖,李硕夏,李泰阳等。则相继而起。诋毁以礼论之外。窃见其意之所在。罔不以先生为厚于昭显。薄于 孝庙而驱之于恶逆也。驱之恶逆。而必欲杀之者。以先生为士林领袖。八方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在朝执政以下。亦多尊信而为先生不惜其发肤者众矣。故先生虽在山野而除去先生。则执政以下自然刊落。正如秋风木叶也。执政以下。落如秋叶。则代执其政者。非渠之徒党而谁耶。以故。百计钻进。指无为有。指白为黑。必欲倾陷。竟遂其计。可谓凶且谲矣。然内无清风府院君金佑明。则外虽有千镌万善道。亦如之何哉。盖清风自犯僭礼。用隧道葬其父僭(一作潜)谷。而被驳之事也。 反仇正士。至以先生为不悦于今 上诞降云。而搆诬行谗。无所不极。则凡可谓为害于先生之言。何所不陈于内乎。想其恒言。必称镌,善道。为君子忠良之人也。宋某则不忠之小人云。而惟 显庙圣德深厚。不即信谗。亦亲见 孝庙之宠擢礼遇之隆重。故不惟不 信谗也。至于 拜相而亲信之矣。然竟不无曾母之投杼。而至 下严批于癸丑。又窜领相(金公寿兴)于甲寅。其窃窥而伺衅者。莫不猬起而鼓舞雀跃。以售其积年忿憾之奸计。此莫非天也。况我 圣上越自幼冲之日。熟闻清风之说。以为宋某乃是不忠之小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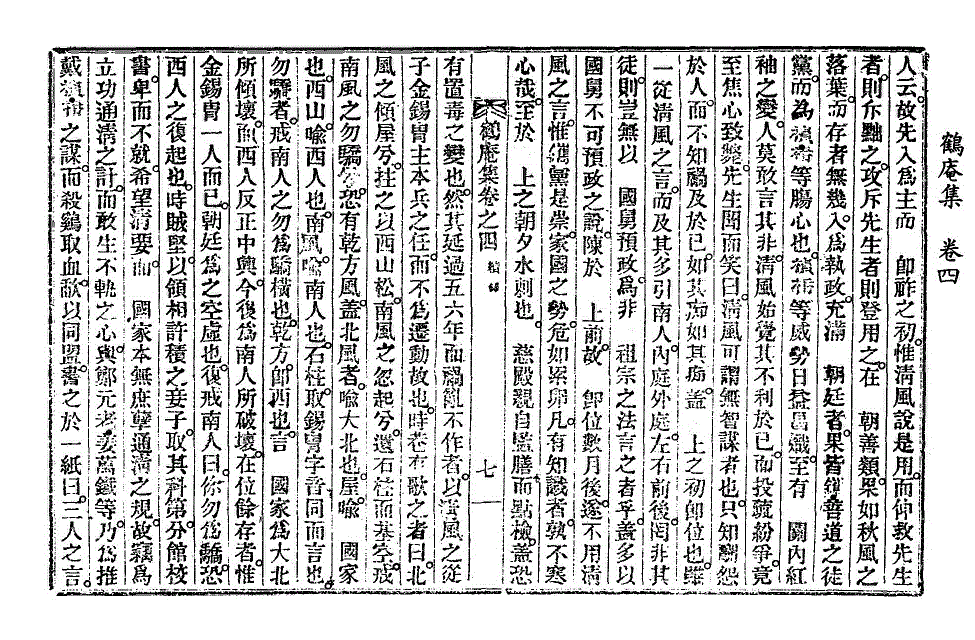 人云。故先入为主而 即祚之初。惟清风说是用。而仲救先生者。则斥黜之。攻斥先生者则登用之。在 朝善类。果如秋风之落叶。而存者无几。入为执政。充满 朝廷者。果皆镌善道之徒党。而为桢,楠等肠心也。桢,楠等威势日益昌炽。至有 关内红袖之变。人莫敢言其非。清风始觉其不利于己。而投疏纷争。竟至焦心致毙。先生闻而笑曰。清风可谓无智谋者也。只知酬怨于人。而不知祸及于己。如其痴如其痴。盖 上之初即位也。虽一从清风之言。而及其多引南人。内庭外庭。左右前后。罔非其徒。则岂无以 国舅预政。为非 祖宗之法言之者乎。盖多以国舅不可预政之说。陈于 上前。故 即位数月后。遂不用清风之言。惟镌党是崇。家国之势。危如累卵。凡有知识者。孰不寒心哉。至于 上之朝夕水刺也。 慈殿亲自监膳而点检。盖恐有置毒之变也。然其延过五六年而祸乱不作者。以清风之从子金锡胄主本兵之任。而不为迁动故也。时巷有歌之者曰。北风之倾屋兮。拄之以西山松。南风之忽起兮。遗石柱而基空。戒南风之勿骄兮。恐有朝方风。盖北风者。喻大北也。屋。喻 国家也。西山。喻西人也。南风。喻南人也。石柱。取锡胄字音同而言也。勿骄者。戒南人之勿为骄横也。乾方。即西也。言 国家为大北所倾坏。而西人反正中兴。今复为南人所破坏。在位馀存者。惟金锡胄一人而已。朝廷为之空虚也。复戒南人曰。你勿为骄。恐西人之复起也。时贼坚。以领相许积之妾子。取其科第。分馆校书。卑而不就。希望清要。而 国家本无庶孽通清之规。故窃为立功通清之计。而敢生不轨之心。与郑元老,姜万铁等。乃为推戴桢,楠之谋。而杀鸡取血。歃以同盟。书之于一纸曰。三人之言。
人云。故先入为主而 即祚之初。惟清风说是用。而仲救先生者。则斥黜之。攻斥先生者则登用之。在 朝善类。果如秋风之落叶。而存者无几。入为执政。充满 朝廷者。果皆镌善道之徒党。而为桢,楠等肠心也。桢,楠等威势日益昌炽。至有 关内红袖之变。人莫敢言其非。清风始觉其不利于己。而投疏纷争。竟至焦心致毙。先生闻而笑曰。清风可谓无智谋者也。只知酬怨于人。而不知祸及于己。如其痴如其痴。盖 上之初即位也。虽一从清风之言。而及其多引南人。内庭外庭。左右前后。罔非其徒。则岂无以 国舅预政。为非 祖宗之法言之者乎。盖多以国舅不可预政之说。陈于 上前。故 即位数月后。遂不用清风之言。惟镌党是崇。家国之势。危如累卵。凡有知识者。孰不寒心哉。至于 上之朝夕水刺也。 慈殿亲自监膳而点检。盖恐有置毒之变也。然其延过五六年而祸乱不作者。以清风之从子金锡胄主本兵之任。而不为迁动故也。时巷有歌之者曰。北风之倾屋兮。拄之以西山松。南风之忽起兮。遗石柱而基空。戒南风之勿骄兮。恐有朝方风。盖北风者。喻大北也。屋。喻 国家也。西山。喻西人也。南风。喻南人也。石柱。取锡胄字音同而言也。勿骄者。戒南人之勿为骄横也。乾方。即西也。言 国家为大北所倾坏。而西人反正中兴。今复为南人所破坏。在位馀存者。惟金锡胄一人而已。朝廷为之空虚也。复戒南人曰。你勿为骄。恐西人之复起也。时贼坚。以领相许积之妾子。取其科第。分馆校书。卑而不就。希望清要。而 国家本无庶孽通清之规。故窃为立功通清之计。而敢生不轨之心。与郑元老,姜万铁等。乃为推戴桢,楠之谋。而杀鸡取血。歃以同盟。书之于一纸曰。三人之言。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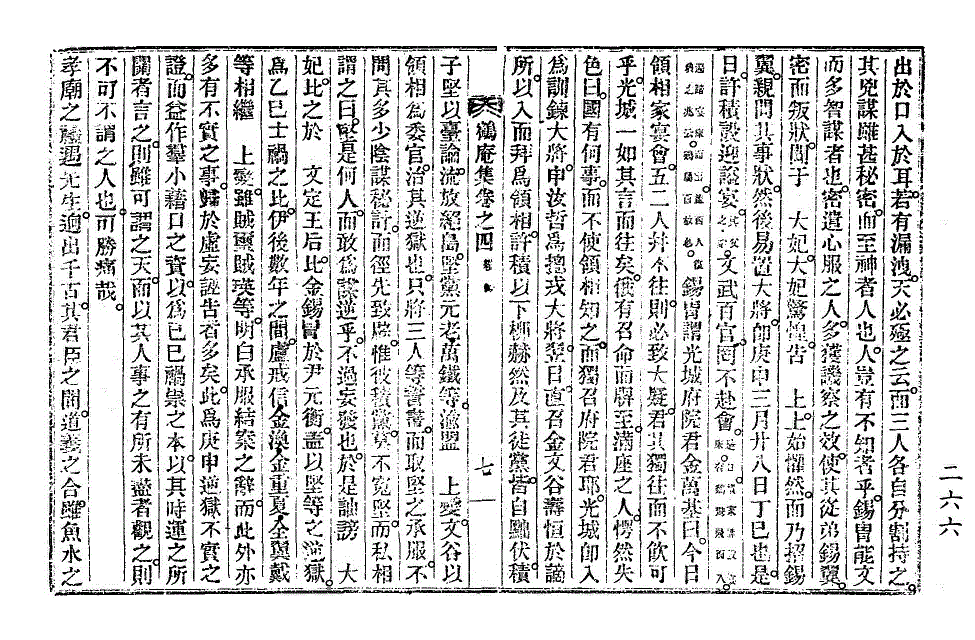 出于口入于耳。若有漏泄。天必殛之云。而三人各自分割持之。其凶谋虽甚秘密。而至神者人也。人岂有不知者乎。锡胄能文而多智谋者也。密遣心服之人。多获讥察之效。使其从弟锡翼。密而叛状。闻于 大妃。大妃惊惶。告 上。上始欢然。而乃招锡翼。亲问其事状。然后易置大将。即庚申三月廿八日丁巳也。是日。许积设迎谥宴。(其父之谥。)文武百官。罔不赴会。(是日。积家排设宴床。有鸡▦飞而入。遍踏宴床而出。盖西人复兴之兆云。鸡属酉故也。)锡胄谓光城府院君金万基曰。今日领相家宴会。五二人并不往。则必致大疑。君其独往而不饮可乎。光城一如其言而往矣。俄有召命而牌至。满座之人。愕然失色曰。国有何事。而不使领相知之。而独召府院君耶。光城即入为训鍊大将。申汝哲为总戎大将。翌日。直召金文谷寿恒于谪所。以入而拜为领相。许积以下柳赫然及其徒党。皆自黜伏。积子坚以台论。流放绝岛。坚党元老,万铁等。渝盟 上变。文谷以领相为委官。治其逆狱也。只将三人等誓书。而取坚之承服。不问其多少阴谋秘计。而径先致辟。惟彼积党。莫不冤坚。而私相谓之曰。坚是何人。而敢为谋逆乎。不过妄发也。于是讪谤 大妃。比之于 文定王后。比金锡冑于尹元衡。盖以坚等之逆狱。为乙巳士祸之比。伊后数年之间。卢戒信,金涣,金重夏,全翼戴等相继 上变。虽贼玺贼瑛等。明白承服结案之辞。而此外亦多有不实之事。归于虚妄诬告者多矣。此为庚申逆狱不实之證。而益作群小藉口之资。以为己巳祸崇之本。以其时运之所关者言之。则虽可谓之天。而以其人事之有所未尽者观之。则不可不谓之人也。可胜痛哉。
出于口入于耳。若有漏泄。天必殛之云。而三人各自分割持之。其凶谋虽甚秘密。而至神者人也。人岂有不知者乎。锡胄能文而多智谋者也。密遣心服之人。多获讥察之效。使其从弟锡翼。密而叛状。闻于 大妃。大妃惊惶。告 上。上始欢然。而乃招锡翼。亲问其事状。然后易置大将。即庚申三月廿八日丁巳也。是日。许积设迎谥宴。(其父之谥。)文武百官。罔不赴会。(是日。积家排设宴床。有鸡▦飞而入。遍踏宴床而出。盖西人复兴之兆云。鸡属酉故也。)锡胄谓光城府院君金万基曰。今日领相家宴会。五二人并不往。则必致大疑。君其独往而不饮可乎。光城一如其言而往矣。俄有召命而牌至。满座之人。愕然失色曰。国有何事。而不使领相知之。而独召府院君耶。光城即入为训鍊大将。申汝哲为总戎大将。翌日。直召金文谷寿恒于谪所。以入而拜为领相。许积以下柳赫然及其徒党。皆自黜伏。积子坚以台论。流放绝岛。坚党元老,万铁等。渝盟 上变。文谷以领相为委官。治其逆狱也。只将三人等誓书。而取坚之承服。不问其多少阴谋秘计。而径先致辟。惟彼积党。莫不冤坚。而私相谓之曰。坚是何人。而敢为谋逆乎。不过妄发也。于是讪谤 大妃。比之于 文定王后。比金锡冑于尹元衡。盖以坚等之逆狱。为乙巳士祸之比。伊后数年之间。卢戒信,金涣,金重夏,全翼戴等相继 上变。虽贼玺贼瑛等。明白承服结案之辞。而此外亦多有不实之事。归于虚妄诬告者多矣。此为庚申逆狱不实之證。而益作群小藉口之资。以为己巳祸崇之本。以其时运之所关者言之。则虽可谓之天。而以其人事之有所未尽者观之。则不可不谓之人也。可胜痛哉。孝庙之礼遇先生。迥出千古。其君臣之间。道义之合。虽鱼水之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7H 页
 之欢。未足以喻其相得之深也。当此之时。岂无群小之媢嫉忮忌者乎。盖已有侧目待衅者矣。况彼尹镌以先生疏远之戚属。初有学名。亦多文艺。先生初与之交。不亦宜乎。见其扫去朱子章句。自作中庸注说。而当而请责。则镌艴然作色曰。子思之意。惟朱子独知。而我不知之耶。其轻侮圣贤。肆然悖慢之状。不忍正视也。先生顾谓在傍者曰。此言何如。在傍者。颇有为镌之语。先生曰。春秋之法。先诛党与君可先被诛责者也。自是之后。疏鑴不亲。故位在铨长。初不举论。尹宣举辈。每书责之以不用镌。先生不得已而拟诸进善之职而除之。宣举犹恨其卑。若完南府院君李公厚源。深责先生曰。何得轻用尹鑴耶。镌父孝全。初亦有令名矣。及为都宪于昏朝也。戕杀君父之子。取其录勋。恶声彰闻矣。今镌虽有学名。安知其不为其父而轻用之耶。先生每思完南之言。而服其有先见之明也。镌果御憾于不大用。而得逢己亥。肆其凶毒矣。尹善道则年长于先生二十岁。而位犹在参议之列。故亦甚快快。祖述镌论。投疏自试。虽被投窜。其党益自御忿。待时而发。不亦怕乎。故人以为 孝庙之礼遇先生。实是为今 上致戮先生。以慰悦豺虎之资也。呜呼痛哉。
之欢。未足以喻其相得之深也。当此之时。岂无群小之媢嫉忮忌者乎。盖已有侧目待衅者矣。况彼尹镌以先生疏远之戚属。初有学名。亦多文艺。先生初与之交。不亦宜乎。见其扫去朱子章句。自作中庸注说。而当而请责。则镌艴然作色曰。子思之意。惟朱子独知。而我不知之耶。其轻侮圣贤。肆然悖慢之状。不忍正视也。先生顾谓在傍者曰。此言何如。在傍者。颇有为镌之语。先生曰。春秋之法。先诛党与君可先被诛责者也。自是之后。疏鑴不亲。故位在铨长。初不举论。尹宣举辈。每书责之以不用镌。先生不得已而拟诸进善之职而除之。宣举犹恨其卑。若完南府院君李公厚源。深责先生曰。何得轻用尹鑴耶。镌父孝全。初亦有令名矣。及为都宪于昏朝也。戕杀君父之子。取其录勋。恶声彰闻矣。今镌虽有学名。安知其不为其父而轻用之耶。先生每思完南之言。而服其有先见之明也。镌果御憾于不大用。而得逢己亥。肆其凶毒矣。尹善道则年长于先生二十岁。而位犹在参议之列。故亦甚快快。祖述镌论。投疏自试。虽被投窜。其党益自御忿。待时而发。不亦怕乎。故人以为 孝庙之礼遇先生。实是为今 上致戮先生。以慰悦豺虎之资也。呜呼痛哉。先生每以为我 孝宗大王有卓冠百王之至德。当作百世不迁之庙云矣。癸亥春。承召入都。 上疏建请。 上命台侍以上集议宾厅。朴世采所论竟不明快矣。及至请加徽号于 太祖大王。以明威化回军尊周大义。则世采极力立异。分明离析。以驯致士祸。以倾危宗社。其罪可胜痛哉。盖栗谷李先生无有师承而自得之矣。世采自拟栗谷。亦无师承云者。乌得免汰哉之诮乎。然位卑而无党援。则来附先辈。不自分岐矣。及其位渐高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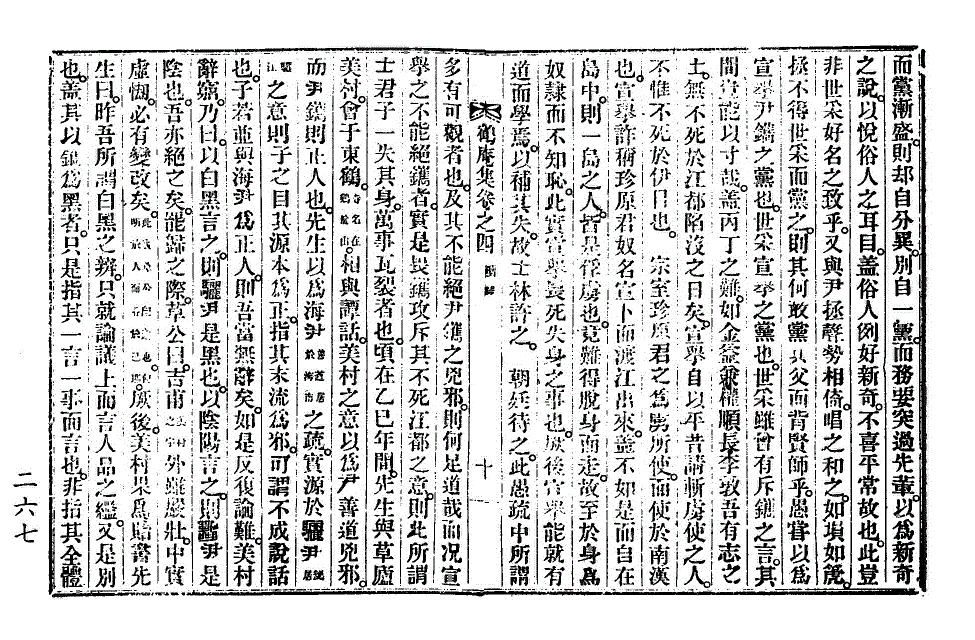 而党渐盛。则却自分异。别自一党。而务要突过先辈。以为新奇之说。以悦俗人之耳目。盖俗人例好新奇。不喜平常故也。此岂非世采好名之致乎。又与尹拯声势相倚。唱之和之。如埙如篪。拯不得世采而党之。则其何敢党其父而背贤师乎。愚尝以为宣举尹镌之党也。世采宣举之党也。世采虽曾有斥镌之言。其间岂能以寸哉。盖丙丁之难。如金益兼,权顺长,李敦吾有志之士。无不死于江都陷没之日矣。宣举自以平昔请斩虏使之人。不惟不死于伊日也。 宗室珍原君之为虏所使。而使于南汉也。宣举诈称珍原君奴名宣卜而渡江出来。盖不如是而自在岛中。则一岛之人。皆是俘虏也。竟难得脱身而走。故至于身为奴隶而不知耻。此实宣举畏死失身之事也。厥后宣举能就有道而举焉。以补其失。故士林许之。 朝廷待之。此愚疏中所谓多有可观者也。及其不能绝尹镌之凶邪。则何足道哉而况宣举之不能绝镌者。实是畏镌攻斥其不死江都之意。则此所谓士君子一失其身。万事瓦裂者也。顷在乙巳年间。先生与草庐美村。会于东鹤。(寺名在鸡龙山。)相与谭话。美村之意以为尹善道凶邪。而尹镌则正人也。先生以为海尹(善道居海南)之疏。实源于骊尹(鑴居骊江)之意则子之目其源本为正。指其末流为邪。可谓不成说话也。子若并与海尹为正人。则吾当无辞矣。如是反复论难。美村辞穷。乃曰。以白黑言之。则骊尹是黑也。以阴阳言之。则骊尹是阴也。吾亦绝之矣。罢归之际。草公曰。吉甫(美村之字)外虽严壮。中实虚怯。必有变改矣。(此实草公自道也。何明于人而昏于己也。)厥后。美村果为贻书先生曰。昨吾所谓白黑之辨。只就论议上而言人品之缆。又是别也。盖其以鑴为黑者。只是指其一言一事而言也。非指其全体
而党渐盛。则却自分异。别自一党。而务要突过先辈。以为新奇之说。以悦俗人之耳目。盖俗人例好新奇。不喜平常故也。此岂非世采好名之致乎。又与尹拯声势相倚。唱之和之。如埙如篪。拯不得世采而党之。则其何敢党其父而背贤师乎。愚尝以为宣举尹镌之党也。世采宣举之党也。世采虽曾有斥镌之言。其间岂能以寸哉。盖丙丁之难。如金益兼,权顺长,李敦吾有志之士。无不死于江都陷没之日矣。宣举自以平昔请斩虏使之人。不惟不死于伊日也。 宗室珍原君之为虏所使。而使于南汉也。宣举诈称珍原君奴名宣卜而渡江出来。盖不如是而自在岛中。则一岛之人。皆是俘虏也。竟难得脱身而走。故至于身为奴隶而不知耻。此实宣举畏死失身之事也。厥后宣举能就有道而举焉。以补其失。故士林许之。 朝廷待之。此愚疏中所谓多有可观者也。及其不能绝尹镌之凶邪。则何足道哉而况宣举之不能绝镌者。实是畏镌攻斥其不死江都之意。则此所谓士君子一失其身。万事瓦裂者也。顷在乙巳年间。先生与草庐美村。会于东鹤。(寺名在鸡龙山。)相与谭话。美村之意以为尹善道凶邪。而尹镌则正人也。先生以为海尹(善道居海南)之疏。实源于骊尹(鑴居骊江)之意则子之目其源本为正。指其末流为邪。可谓不成说话也。子若并与海尹为正人。则吾当无辞矣。如是反复论难。美村辞穷。乃曰。以白黑言之。则骊尹是黑也。以阴阳言之。则骊尹是阴也。吾亦绝之矣。罢归之际。草公曰。吉甫(美村之字)外虽严壮。中实虚怯。必有变改矣。(此实草公自道也。何明于人而昏于己也。)厥后。美村果为贻书先生曰。昨吾所谓白黑之辨。只就论议上而言人品之缆。又是别也。盖其以鑴为黑者。只是指其一言一事而言也。非指其全体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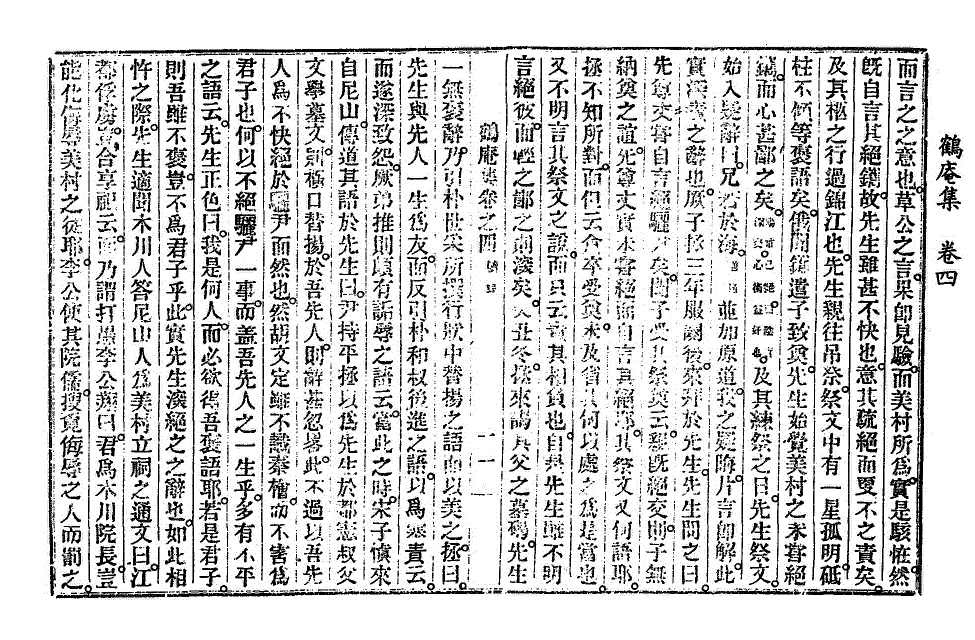 而言之之意也。草公之言。果即见验。而美村所为。实是骇怪。然既自言其绝镌。故先生虽甚不快也。意其疏绝而更不之责矣。及其柩之行过锦江也。先生亲往吊祭。祭文中有一星孤明。砥柱不倾等褒语矣。俄闻镌遣子致奠。先生始觉美村之未尝绝镌。而心甚鄙之矣。(阳示已绝。而阴实深交。心术益奸也。)及其练祭之日。先生祭文。始入疑辞曰。兄若于海。(善道)并加原道。我之疑晦。片言即解。此实深责之辞也。厥子拯三年服阕后。来拜于先生。先生问之曰。先尊交尝自言绝骊尹矣。闻子受其祭奠云。亲既绝交。则子无纳奠之谊。先尊丈实未尝绝而自言其绝耶。其祭文又何语耶。拯不知所对。而但云仓卒受奠。未及省其何以处之为是当也。又不明言其祭文之说。而只云责其相负也。自是先生虽不明言绝彼。而轻之鄙之则深矣。癸丑冬。拯来谒其父之墓碣。先生一无褒辞。乃引朴世采所撰行状中替扬之语而以美之。拯曰。先生与先人一生为友。而反引朴和叔后进之语。以为塞责云。而遂深致怨。厥弟推则颇有诟辱之语云。当此之时。宋子慎来自尼山。传道其语于先生曰。尹持平拯以为先生于都宪叔父文举墓文。则极口替扬。于吾先人。则辞甚忽略。此不过以吾先人为不快绝于骊尹而然也。然胡文定虽不识秦桧。而不害为君子也。何以不绝骊尹一事。而盖吾先人之一生乎。多有不平之语云。先生正色曰。我是何人。而必欲得吾褒语耶。若是君子。则吾虽不褒。岂不为君子乎。此实先生深绝之之辞也。如此相忤之际。先生适闻木川人答尼山人为美村立祠之通文曰。江都俘虏。岂合享祀云。而乃谓打愚李公翔曰。君为木川院长。岂能化侮辱美村之徒耶。李公使其院儒。搜觅侮辱之人而罚之。
而言之之意也。草公之言。果即见验。而美村所为。实是骇怪。然既自言其绝镌。故先生虽甚不快也。意其疏绝而更不之责矣。及其柩之行过锦江也。先生亲往吊祭。祭文中有一星孤明。砥柱不倾等褒语矣。俄闻镌遣子致奠。先生始觉美村之未尝绝镌。而心甚鄙之矣。(阳示已绝。而阴实深交。心术益奸也。)及其练祭之日。先生祭文。始入疑辞曰。兄若于海。(善道)并加原道。我之疑晦。片言即解。此实深责之辞也。厥子拯三年服阕后。来拜于先生。先生问之曰。先尊交尝自言绝骊尹矣。闻子受其祭奠云。亲既绝交。则子无纳奠之谊。先尊丈实未尝绝而自言其绝耶。其祭文又何语耶。拯不知所对。而但云仓卒受奠。未及省其何以处之为是当也。又不明言其祭文之说。而只云责其相负也。自是先生虽不明言绝彼。而轻之鄙之则深矣。癸丑冬。拯来谒其父之墓碣。先生一无褒辞。乃引朴世采所撰行状中替扬之语而以美之。拯曰。先生与先人一生为友。而反引朴和叔后进之语。以为塞责云。而遂深致怨。厥弟推则颇有诟辱之语云。当此之时。宋子慎来自尼山。传道其语于先生曰。尹持平拯以为先生于都宪叔父文举墓文。则极口替扬。于吾先人。则辞甚忽略。此不过以吾先人为不快绝于骊尹而然也。然胡文定虽不识秦桧。而不害为君子也。何以不绝骊尹一事。而盖吾先人之一生乎。多有不平之语云。先生正色曰。我是何人。而必欲得吾褒语耶。若是君子。则吾虽不褒。岂不为君子乎。此实先生深绝之之辞也。如此相忤之际。先生适闻木川人答尼山人为美村立祠之通文曰。江都俘虏。岂合享祀云。而乃谓打愚李公翔曰。君为木川院长。岂能化侮辱美村之徒耶。李公使其院儒。搜觅侮辱之人而罚之。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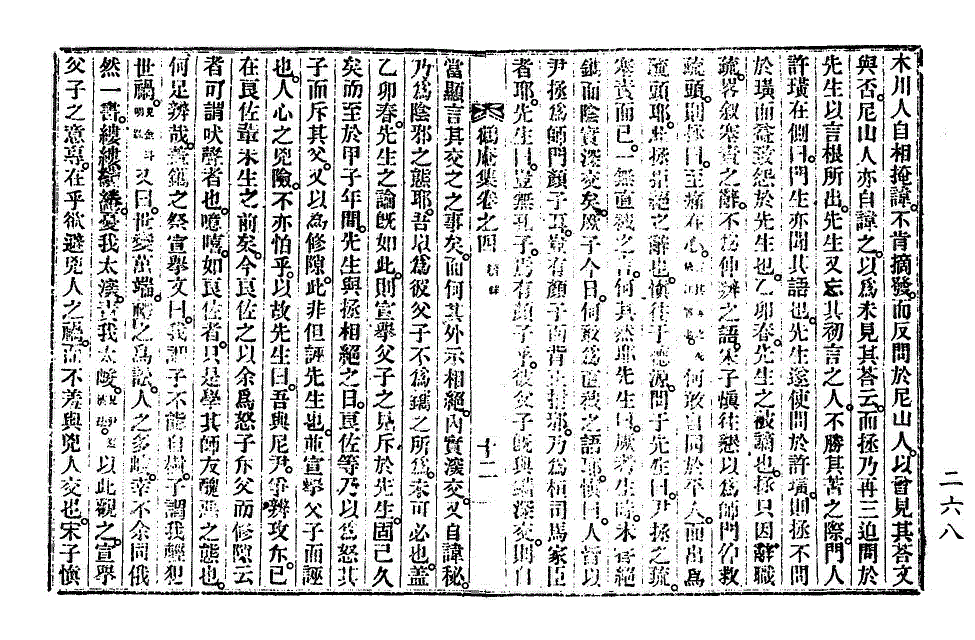 木川人自相掩讳。不肯摘发。而反问于尼山人。以曾见其答文与否。尼山人亦自讳之。以为未见其答云。而拯乃再三迫问于先生以言根所出。先生又忘其初言之人。不胜其苦之际。门人许璜在侧曰。门生亦闻其语也。先生遂使问于许璜。则拯不问于璜而益致怨于先生也。乙卯春。先生之被谪也。拯只因辞职疏。略叙塞责之辞。不为伸辨之语。宋子慎往恳以为师门伸救疏头。则拯曰。至痛在心。(言其母之死于江都也。)何敢自同于平人。而出为疏头耶。此拯拒绝之辞也。慎往于德源。问于先生曰。尹拯之疏。塞责而已。一无直截之言。何其然耶。先生曰。厥考生时。未尝绝镌而阴实深交矣。厥子今日。何敢为直截之语耶。慎曰。人皆以尹拯为师门颜子耳。岂有颜子而背正拊邪。乃为桓司马家臣者耶。先生曰。岂无孔子。焉有颜子乎。彼父子既与鑴深交。则自当显言其交之之事矣。而何其外示相绝。内实深交。又自讳秘。乃为阴邪之态耶。吾以为彼父子不为镌之所为。未可必也。盖乙卯春。先生之论既如此。则宣举父子之见斥于先生。固已久矣而至于甲子年间。先生与拯相绝之日。良佐等乃以为怒其子而斥其父。又以为修隙。此非但诬先生也。并宣举父子而诬也。人心之凶险。不亦怕乎。以故先生曰。吾与尼尹。争辨攻斥。已在良佐辈未生之前矣。今良佐之以余为怒子斥父而修隙云者可谓吠声者也。噫嘻。如良佐者。只是学其师友丑恶之态也。何足辨哉。盖镌之祭宣举文曰。我谓子不能自树。子谓我轻犯世祸。(见金斗明疏)又曰。世变万端。礼之为讼。人之多岐。幸不余同俄然一书。缕缕缱绻。忧我太深。责我太峻。(见尹夏济疏。)以此观之。宣举父子之意。专在乎欲避凶人之祸。而不羞与凶人交也。宋子慎
木川人自相掩讳。不肯摘发。而反问于尼山人。以曾见其答文与否。尼山人亦自讳之。以为未见其答云。而拯乃再三迫问于先生以言根所出。先生又忘其初言之人。不胜其苦之际。门人许璜在侧曰。门生亦闻其语也。先生遂使问于许璜。则拯不问于璜而益致怨于先生也。乙卯春。先生之被谪也。拯只因辞职疏。略叙塞责之辞。不为伸辨之语。宋子慎往恳以为师门伸救疏头。则拯曰。至痛在心。(言其母之死于江都也。)何敢自同于平人。而出为疏头耶。此拯拒绝之辞也。慎往于德源。问于先生曰。尹拯之疏。塞责而已。一无直截之言。何其然耶。先生曰。厥考生时。未尝绝镌而阴实深交矣。厥子今日。何敢为直截之语耶。慎曰。人皆以尹拯为师门颜子耳。岂有颜子而背正拊邪。乃为桓司马家臣者耶。先生曰。岂无孔子。焉有颜子乎。彼父子既与鑴深交。则自当显言其交之之事矣。而何其外示相绝。内实深交。又自讳秘。乃为阴邪之态耶。吾以为彼父子不为镌之所为。未可必也。盖乙卯春。先生之论既如此。则宣举父子之见斥于先生。固已久矣而至于甲子年间。先生与拯相绝之日。良佐等乃以为怒其子而斥其父。又以为修隙。此非但诬先生也。并宣举父子而诬也。人心之凶险。不亦怕乎。以故先生曰。吾与尼尹。争辨攻斥。已在良佐辈未生之前矣。今良佐之以余为怒子斥父而修隙云者可谓吠声者也。噫嘻。如良佐者。只是学其师友丑恶之态也。何足辨哉。盖镌之祭宣举文曰。我谓子不能自树。子谓我轻犯世祸。(见金斗明疏)又曰。世变万端。礼之为讼。人之多岐。幸不余同俄然一书。缕缕缱绻。忧我太深。责我太峻。(见尹夏济疏。)以此观之。宣举父子之意。专在乎欲避凶人之祸。而不羞与凶人交也。宋子慎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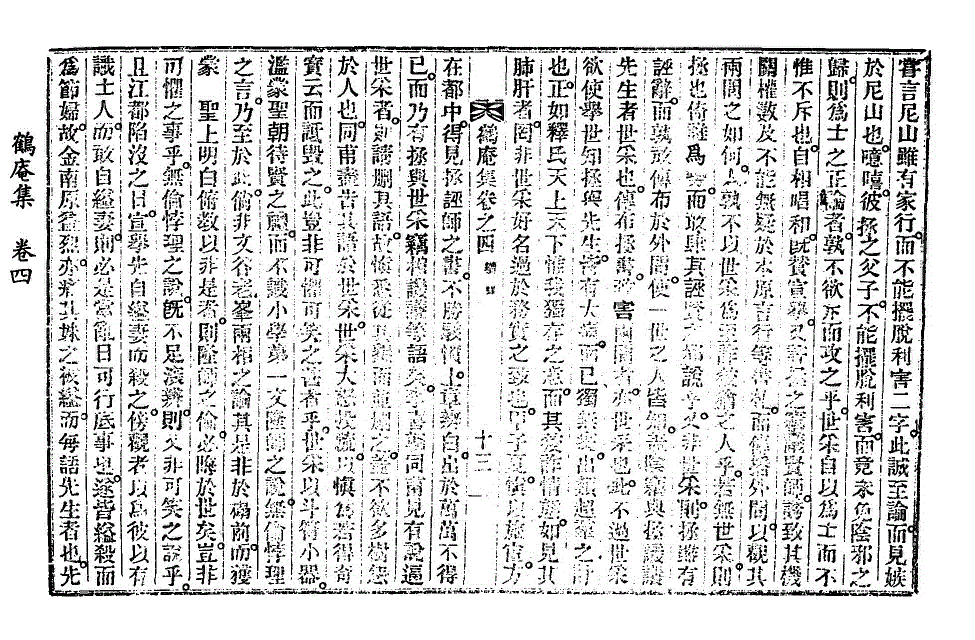 尝言尼山虽有家行。而不能摆脱利害二字。此诚至论。而见嫉于尼山也。噫嘻。彼拯之父子。不能摆脱利害。而竟未免阴邪之归。则为士之正论者。孰不欲斥而攻之乎。世采自以为士而不惟不斥也。自相唱和。既赞宣举。又许拯之窃议贤师。诱致其机关权数及不能无疑于本原言行等书札。而传播外问。以观其两间之如何。人孰不以世采为至诈狡狯之人乎。若无世采。则拯也倚谁为势。而敢肆其诬贤之邪说乎。又非世采。则拯虽有诬辞。而孰放传布于外间。使一世之人皆知。盖阴窃与拯讥议先生者世采也。传布拯书。致害两间者。亦世采也。此不过世采欲使举世知拯与先生。皆有大病。而己独无疵。出类超群之计也。正如释氏天上天下惟我独存之意。而其狡诈情态。如见其肺肝者。罔非世采好名过于务实之致也。甲子夏。慎以旅宦。方在都中。得见拯诬师之书。不胜骇愤。上章辨白。出于万万不得已。而乃有拯与世采窃相讥议等语矣。李喜朝同甫见有说逼世采者。则请删其语。故慎悉从其恳而并删之。盖不欲多树怨于人也。同甫尽告其语于世采。世采大怒投疏。以慎为若得奇宝云而诋毁之。此岂非可惧可笑之甚者乎。世采以斗筲小器。滥蒙圣朝待贤之礼。而不识小学第一文隆师之说。无伦悖理之言。乃至于此。倘非文谷老峰两相之论其是非于榻前。而获蒙 圣上明白俯教以非是者。则隆师之伦。必晦于世矣。岂非可惧之事乎。无伦悖理之说。既不足深辨。则又非可笑之说乎。且江都陷没之日。宣举先自缢妻而杀之。傍观者以为彼以有识士人。而敢自缢妻。则必是当乱日可行底事也。遂皆缢杀而为节妇。故金南原益烈。亦痛其妹之被缢。而每语先生者也。先
尝言尼山虽有家行。而不能摆脱利害二字。此诚至论。而见嫉于尼山也。噫嘻。彼拯之父子。不能摆脱利害。而竟未免阴邪之归。则为士之正论者。孰不欲斥而攻之乎。世采自以为士而不惟不斥也。自相唱和。既赞宣举。又许拯之窃议贤师。诱致其机关权数及不能无疑于本原言行等书札。而传播外问。以观其两间之如何。人孰不以世采为至诈狡狯之人乎。若无世采。则拯也倚谁为势。而敢肆其诬贤之邪说乎。又非世采。则拯虽有诬辞。而孰放传布于外间。使一世之人皆知。盖阴窃与拯讥议先生者世采也。传布拯书。致害两间者。亦世采也。此不过世采欲使举世知拯与先生。皆有大病。而己独无疵。出类超群之计也。正如释氏天上天下惟我独存之意。而其狡诈情态。如见其肺肝者。罔非世采好名过于务实之致也。甲子夏。慎以旅宦。方在都中。得见拯诬师之书。不胜骇愤。上章辨白。出于万万不得已。而乃有拯与世采窃相讥议等语矣。李喜朝同甫见有说逼世采者。则请删其语。故慎悉从其恳而并删之。盖不欲多树怨于人也。同甫尽告其语于世采。世采大怒投疏。以慎为若得奇宝云而诋毁之。此岂非可惧可笑之甚者乎。世采以斗筲小器。滥蒙圣朝待贤之礼。而不识小学第一文隆师之说。无伦悖理之言。乃至于此。倘非文谷老峰两相之论其是非于榻前。而获蒙 圣上明白俯教以非是者。则隆师之伦。必晦于世矣。岂非可惧之事乎。无伦悖理之说。既不足深辨。则又非可笑之说乎。且江都陷没之日。宣举先自缢妻而杀之。傍观者以为彼以有识士人。而敢自缢妻。则必是当乱日可行底事也。遂皆缢杀而为节妇。故金南原益烈。亦痛其妹之被缢。而每语先生者也。先鹤庵集卷之四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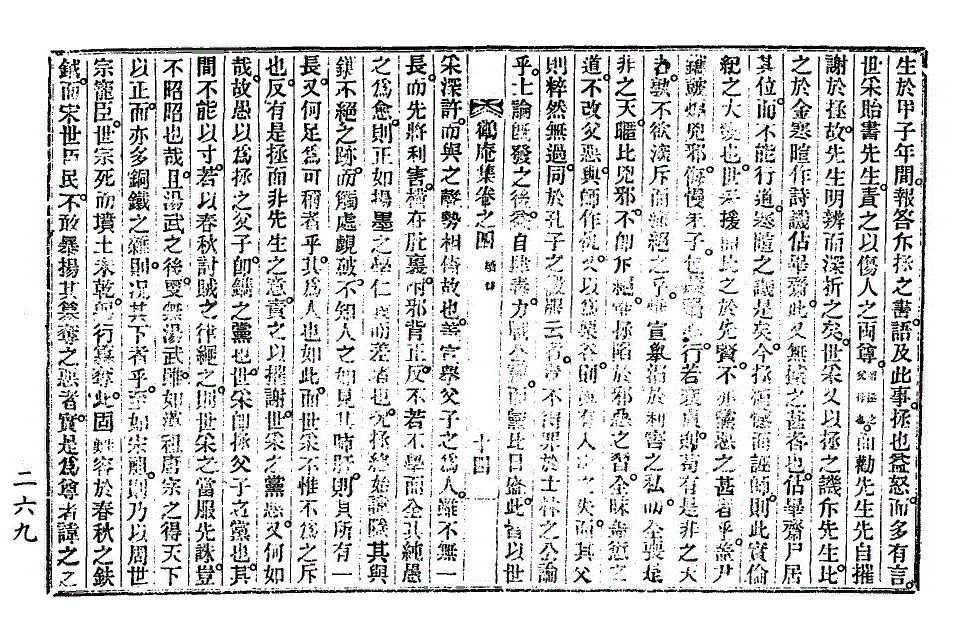 生于甲子年间。报答斥拯之书。语及此事。拯也益怒。而多有言。世采贻书先生。责之以伤人之两尊。(谓拯之父母也。)而劝先生先自摧谢于拯。故先生明辨而深折(一作析)之矣。世采又以拯之议斥先生。比之于金寒暄作诗讥佔毕斋。此又无据之甚者也。佔毕斋尸居其位。而不能行道。寒暄之讥是矣。今拯御憾而诬师。则此实伦纪之大变也。世采援而比之于先贤。不亦党恶之甚者乎。盖尹镌鼓煽凶邪。侮慢朱子。包藏祸心。行若衮贞。则苟有是非之大者。孰不欲深斥而痛绝之乎。惟宣举汨于利害之私。而全丧是非之天。昵比凶邪。不即斥绝。惟拯陷于邪恶之习。全昩盖愆之道。不改父恶。与师作仇。又以为栗谷。则真有入山之失。而其父则粹然无过。同于孔子之微服云者。岂不得罪于士林之公论乎。士论既发之后。益自肆毒。力战公议。而党比日盛。此皆以世采深许。而与之声势相倚故也。盖宣举父子之为人。虽不无一长。而先将利害。横在肚里。附邪背正。反不若不学而全其纯愚之为愈。则正如场墨之学仁义而差者也。况拯终始讳隐其与镌不绝之迹。而触处觑破。不知人之如见其肺肝。则其所有一长。又何足为可称者乎。其为人也如此。而世采不惟不为之斥也。反有是拯而非先生之意。责之以摧谢。世采之党恶。又何如哉。故愚以为拯之父子。即镌之党也。世采即拯父子之党也。其间不能以寸。若以春秋讨贼之律绳之。则世采之当服先诛。岂不昭昭也哉。且汤武之后。更无汤武。虽如汉祖唐宗之得天下以正。而亦多铜铁之杂。则况其下者乎。至如宋祖。则乃以周世宗宠臣。世宗死而坟土未乾。穷行篡夺。此固难容于春秋之鈇銊。而宋世臣民。不敢暴扬其篡夺之恶者。实是为尊者讳之之
生于甲子年间。报答斥拯之书。语及此事。拯也益怒。而多有言。世采贻书先生。责之以伤人之两尊。(谓拯之父母也。)而劝先生先自摧谢于拯。故先生明辨而深折(一作析)之矣。世采又以拯之议斥先生。比之于金寒暄作诗讥佔毕斋。此又无据之甚者也。佔毕斋尸居其位。而不能行道。寒暄之讥是矣。今拯御憾而诬师。则此实伦纪之大变也。世采援而比之于先贤。不亦党恶之甚者乎。盖尹镌鼓煽凶邪。侮慢朱子。包藏祸心。行若衮贞。则苟有是非之大者。孰不欲深斥而痛绝之乎。惟宣举汨于利害之私。而全丧是非之天。昵比凶邪。不即斥绝。惟拯陷于邪恶之习。全昩盖愆之道。不改父恶。与师作仇。又以为栗谷。则真有入山之失。而其父则粹然无过。同于孔子之微服云者。岂不得罪于士林之公论乎。士论既发之后。益自肆毒。力战公议。而党比日盛。此皆以世采深许。而与之声势相倚故也。盖宣举父子之为人。虽不无一长。而先将利害。横在肚里。附邪背正。反不若不学而全其纯愚之为愈。则正如场墨之学仁义而差者也。况拯终始讳隐其与镌不绝之迹。而触处觑破。不知人之如见其肺肝。则其所有一长。又何足为可称者乎。其为人也如此。而世采不惟不为之斥也。反有是拯而非先生之意。责之以摧谢。世采之党恶。又何如哉。故愚以为拯之父子。即镌之党也。世采即拯父子之党也。其间不能以寸。若以春秋讨贼之律绳之。则世采之当服先诛。岂不昭昭也哉。且汤武之后。更无汤武。虽如汉祖唐宗之得天下以正。而亦多铜铁之杂。则况其下者乎。至如宋祖。则乃以周世宗宠臣。世宗死而坟土未乾。穷行篡夺。此固难容于春秋之鈇銊。而宋世臣民。不敢暴扬其篡夺之恶者。实是为尊者讳之之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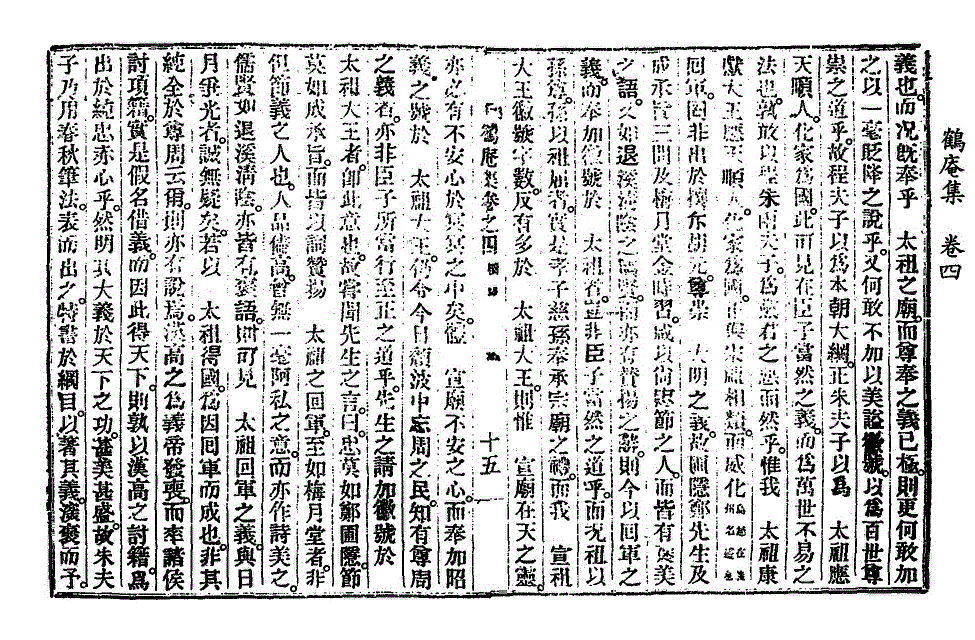 义也。而况既奉乎 太祖之庙。而尊奉之义已极。则更何敢加之以一毫贬降之说乎。又何敢不加以美谥徽号。以为百世尊崇之道乎。故程夫子以为本朝大纲。正朱夫子以为 太祖应天顺人。化家为国。此可见在臣子当然之义。而为万世不易之法也。孰敢以程两夫子。为党君之恶而然乎。惟我 太祖康献大王应天顺人。化家为国。正与宋朝相类。而威化(岛越在义州名边也)回军。罔非出于攘斥胡元。尊崇 大明之义。故圃隐郑先生及成承旨三问及梅月堂金时习。咸以尚忠节之人。而皆有褒美之语。又如退溪清阴之儒贤。而亦有赞扬之辞。则今以回军之义。而奉加德号于 太祖者。岂非臣子当然之道乎。而况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者。实是孝子慈孙奉承宗庙之礼。而我 宣祖大王徽号字数。反有多于 太祖大王。则惟 宣庙在天之灵。亦必有不安心于冥冥之中矣。体 宣庙不安之心。而奉加昭义之号于 太祖大王。仍令今日颓波中忘周之民。知有尊周之义者。亦非臣子所当行至正之道乎。先生之请加徽号于 太祖大王者。即此意也。故尝闻先生之言。曰。忠莫如郑圃隐。节莫如成承旨。而皆以词赞扬 太祖之回军。至如梅月堂者。非但节义之人也。人品尽高。曾无一毫阿私之意。而亦作诗美之。儒贤如退溪清阴。亦皆有褒语。则可见 太祖回军之义。与日月争光者。诚无疑矣。若以 太祖得国。为因回军而成也。非其纯全于尊周云尔。则亦有说焉。汉高之为义帝发丧。而率诸侯讨项籍。实是假名借义。而因此得天下。则孰以汉高之讨籍。为出于纯忠赤心乎。然明其大义于天下之功。甚美甚盛。故朱夫子乃用春秋笔法。表而出之。特书于纲目。以著其义。深褒而予。
义也。而况既奉乎 太祖之庙。而尊奉之义已极。则更何敢加之以一毫贬降之说乎。又何敢不加以美谥徽号。以为百世尊崇之道乎。故程夫子以为本朝大纲。正朱夫子以为 太祖应天顺人。化家为国。此可见在臣子当然之义。而为万世不易之法也。孰敢以程两夫子。为党君之恶而然乎。惟我 太祖康献大王应天顺人。化家为国。正与宋朝相类。而威化(岛越在义州名边也)回军。罔非出于攘斥胡元。尊崇 大明之义。故圃隐郑先生及成承旨三问及梅月堂金时习。咸以尚忠节之人。而皆有褒美之语。又如退溪清阴之儒贤。而亦有赞扬之辞。则今以回军之义。而奉加德号于 太祖者。岂非臣子当然之道乎。而况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者。实是孝子慈孙奉承宗庙之礼。而我 宣祖大王徽号字数。反有多于 太祖大王。则惟 宣庙在天之灵。亦必有不安心于冥冥之中矣。体 宣庙不安之心。而奉加昭义之号于 太祖大王。仍令今日颓波中忘周之民。知有尊周之义者。亦非臣子所当行至正之道乎。先生之请加徽号于 太祖大王者。即此意也。故尝闻先生之言。曰。忠莫如郑圃隐。节莫如成承旨。而皆以词赞扬 太祖之回军。至如梅月堂者。非但节义之人也。人品尽高。曾无一毫阿私之意。而亦作诗美之。儒贤如退溪清阴。亦皆有褒语。则可见 太祖回军之义。与日月争光者。诚无疑矣。若以 太祖得国。为因回军而成也。非其纯全于尊周云尔。则亦有说焉。汉高之为义帝发丧。而率诸侯讨项籍。实是假名借义。而因此得天下。则孰以汉高之讨籍。为出于纯忠赤心乎。然明其大义于天下之功。甚美甚盛。故朱夫子乃用春秋笔法。表而出之。特书于纲目。以著其义。深褒而予。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0L 页
 以此惟之。则今我 太祖虽因此回军而得国。然其不敢犯 大明而回军者。实是尊周莫大之义。则后世继朱子而秉史笔者。必且深褒而特书之义。昭然无疑矣。朴和叔独于此立异。而力防 徽号之上。实未晓其意之所在也。且若非今日。则吾亦何敢必请此事于 朝乎。今日之人。甘心事虏。不复知有尊周之义。故因此而欲使今人知有尊周之义也。先生此语。实出于孔子衰世之意。而临终之言。亦且如是。而一毫不爽于当日之言。则此可见先生至诚尊周之义。盖无间于死生之际也。其可以先生 徽号之请。为党君之恶乎。彼必欲背于先生而立异者。不亦怪忘颇僻之甚者乎。以故。老峰闵丈亦曰。朴和叔之言若行。则尤丈之言。不行而必去矣。和叔逐尤丈而独留为国耶。其心未可知也。当时善类之言。皆如此尔。若因朴说而渐至于不复知有 大明之尊。则几何其沦胥于夷狄禽兽之归耶。世采之极力立异于此。而防塞 徽号于榻前者。意非寻常。而其徒誇之以清论。骤而听之者。亦以其新奇而悦之。然世采若是丽氏之臣。则可为清论可为节义也。身事我 朝。则何敢以 太祖之得国为非而贬之乎。至于其子泰殷。则对先生出示中原人贬斥 太祖之书。此实其父之意也。先生不见其书而归语人曰。不幸今日见王雱。(雱即安石之子。囚首徒跣常在安石之侧。力主其父之论。而对客者也。)其警责可谓严矣。世采固非病风丧心底人也。岂有推戴丽氏之心而然乎。只是好名之心胜。务实之意少。故乃为新奇之说。务要突过前辈。而不自知其犯乎不韪之罪也。率其徒象。分岐作党。自谓公论。显护逆党。以为日后保身之地。而竟能脱祸于今日。则亦可谓诈诘之甚者也。诈诘之甚。而以开凶党杀贤之
以此惟之。则今我 太祖虽因此回军而得国。然其不敢犯 大明而回军者。实是尊周莫大之义。则后世继朱子而秉史笔者。必且深褒而特书之义。昭然无疑矣。朴和叔独于此立异。而力防 徽号之上。实未晓其意之所在也。且若非今日。则吾亦何敢必请此事于 朝乎。今日之人。甘心事虏。不复知有尊周之义。故因此而欲使今人知有尊周之义也。先生此语。实出于孔子衰世之意。而临终之言。亦且如是。而一毫不爽于当日之言。则此可见先生至诚尊周之义。盖无间于死生之际也。其可以先生 徽号之请。为党君之恶乎。彼必欲背于先生而立异者。不亦怪忘颇僻之甚者乎。以故。老峰闵丈亦曰。朴和叔之言若行。则尤丈之言。不行而必去矣。和叔逐尤丈而独留为国耶。其心未可知也。当时善类之言。皆如此尔。若因朴说而渐至于不复知有 大明之尊。则几何其沦胥于夷狄禽兽之归耶。世采之极力立异于此。而防塞 徽号于榻前者。意非寻常。而其徒誇之以清论。骤而听之者。亦以其新奇而悦之。然世采若是丽氏之臣。则可为清论可为节义也。身事我 朝。则何敢以 太祖之得国为非而贬之乎。至于其子泰殷。则对先生出示中原人贬斥 太祖之书。此实其父之意也。先生不见其书而归语人曰。不幸今日见王雱。(雱即安石之子。囚首徒跣常在安石之侧。力主其父之论。而对客者也。)其警责可谓严矣。世采固非病风丧心底人也。岂有推戴丽氏之心而然乎。只是好名之心胜。务实之意少。故乃为新奇之说。务要突过前辈。而不自知其犯乎不韪之罪也。率其徒象。分岐作党。自谓公论。显护逆党。以为日后保身之地。而竟能脱祸于今日。则亦可谓诈诘之甚者也。诈诘之甚。而以开凶党杀贤之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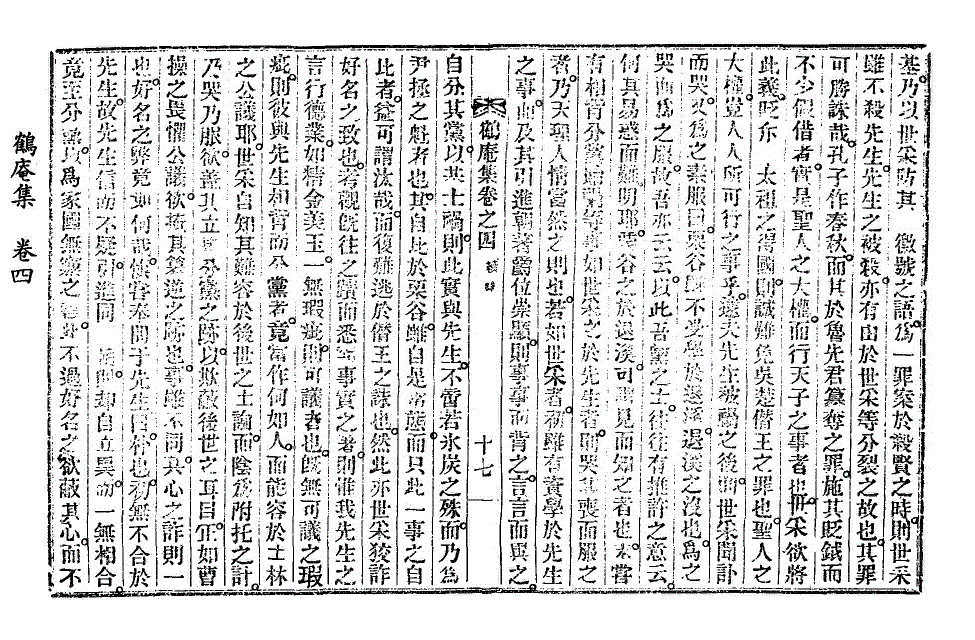 基。乃以世采防其 徽号之语。为一罪案于杀贤之时。则世采虽不杀先生。先生之被杀。亦有由于世采等分裂之故也。其罪可胜诛哉。孔子作春秋。而其于鲁先君篡夺之罪。施其贬銊而不少假借者。实是圣人之大权。而行天子之事者也。世采欲将此义。贬斥 太祖之得国。则诚虽免吴楚僭王之罪也。圣人之大权。岂人人所可行之事乎。逮夫先生被祸之后。则世采闻讣而哭。又为之素服曰。栗谷虽不受学于退溪。退溪之没也。为之哭而为之服。故吾亦云云。以此吾党之士。往往有推许之意云。何其易惑而难明耶。栗谷之于退溪。可谓见而知之者也。未尝有相背分党贻祸等事如世采之于先生者。则哭其丧而服之者。乃天理人情当然之则也。若如世采者。初虽有资学于先生之事。而及其引进朝著爵位崇显。则事事而背之。言言而异之。自分其党。以共士祸。则此实与先生。不啻若冰炭之殊。而乃为尹拯之魁者也。其自比于栗谷。虽自是▦熊。而只此一事之自比者。益可谓汰哉。而复难逃于僭王之诛也。然此亦世采狡诈好名之致也。考观既往之迹而悉闻事实之者。则惟我先生之言行德业。如精金美玉。一无瑕疵。则可议者也。既无可议之瑕疵。则彼与先生相背而分党者。竟富作何如人。而能容于士林之公议耶。世采自知其难容于后世之土论。而阴为附托之计。乃哭乃服。欲盖其立▦分党之迹。以欺蔽后世之耳目。正如曹操之畏惧公议。欲掩其篡逆之迹也。事虽不同。其心之诈则一也。好名之弊竟如何哉。慎尝奉问于先生曰。朴也。初无不合于先生。故先生信而不疑。引进同 朝。则却自立异。而一无相合。竟至分党。以为家国无穷之害。此不过好名之欲蔽其心。而不
基。乃以世采防其 徽号之语。为一罪案于杀贤之时。则世采虽不杀先生。先生之被杀。亦有由于世采等分裂之故也。其罪可胜诛哉。孔子作春秋。而其于鲁先君篡夺之罪。施其贬銊而不少假借者。实是圣人之大权。而行天子之事者也。世采欲将此义。贬斥 太祖之得国。则诚虽免吴楚僭王之罪也。圣人之大权。岂人人所可行之事乎。逮夫先生被祸之后。则世采闻讣而哭。又为之素服曰。栗谷虽不受学于退溪。退溪之没也。为之哭而为之服。故吾亦云云。以此吾党之士。往往有推许之意云。何其易惑而难明耶。栗谷之于退溪。可谓见而知之者也。未尝有相背分党贻祸等事如世采之于先生者。则哭其丧而服之者。乃天理人情当然之则也。若如世采者。初虽有资学于先生之事。而及其引进朝著爵位崇显。则事事而背之。言言而异之。自分其党。以共士祸。则此实与先生。不啻若冰炭之殊。而乃为尹拯之魁者也。其自比于栗谷。虽自是▦熊。而只此一事之自比者。益可谓汰哉。而复难逃于僭王之诛也。然此亦世采狡诈好名之致也。考观既往之迹而悉闻事实之者。则惟我先生之言行德业。如精金美玉。一无瑕疵。则可议者也。既无可议之瑕疵。则彼与先生相背而分党者。竟富作何如人。而能容于士林之公议耶。世采自知其难容于后世之土论。而阴为附托之计。乃哭乃服。欲盖其立▦分党之迹。以欺蔽后世之耳目。正如曹操之畏惧公议。欲掩其篡逆之迹也。事虽不同。其心之诈则一也。好名之弊竟如何哉。慎尝奉问于先生曰。朴也。初无不合于先生。故先生信而不疑。引进同 朝。则却自立异。而一无相合。竟至分党。以为家国无穷之害。此不过好名之欲蔽其心。而不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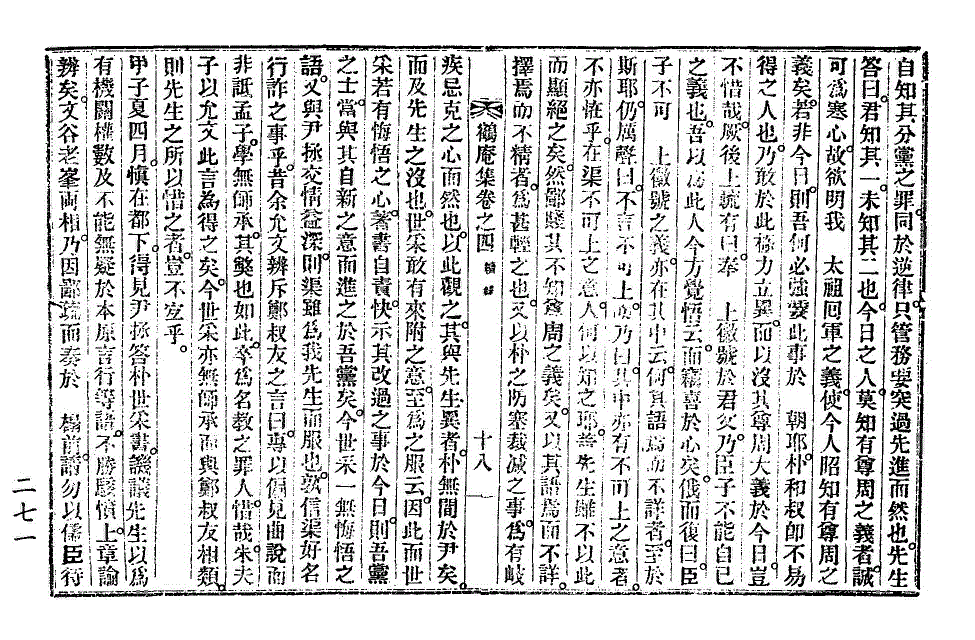 自知其分党之罪。同于逆律。只管务要突过先进而然也。先生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日之人。莫知有尊周之义者。诚可为寒心。故欲明我 太祖回军之义。使今人昭知有尊周之义矣。若非今日。则吾何必强要此事于 朝耶。朴和叔即不易得之人也。乃敢于此极力立异。而以没其尊周大义于今日。岂不惜哉。厥后上疏有曰。奉 上徽号于君父。乃臣子不能自已之义也。吾以为此人今方觉悟云。而窃喜于心矣。俄而复曰。臣子不可 上徽号之义。亦在其中云。何其语焉而不详者。至于斯耶。仍厉声曰。不言不可上。而乃曰。其中亦有不可上之意者。不亦怪乎。在渠不可上之意。人何以知之耶。盖先生虽不以此而显绝之矣。然鄙贱其不知尊周之义矣。又以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为甚轻之也。又以朴之防塞裁减之事。为有岐疾忌克之心而然也。以此观之。其与先生异者。朴无间于尹矣。而及先生之没也。世采敢有来附之意。至为之服云。因此而世采若有悔悟之心。著书自责。快示其改过之事于今日。则吾党之士。当与其自新之意而进之于吾党矣。今世采一无悔悟之语。又与尹拯交情益深。则渠虽为我先生而服也。孰信渠好名行诈之事乎。昔余允文辨斥郑叔友之言曰。专以偏见曲说而非诋孟子。学无师承。其弊也如此。卒为名教之罪人。惜哉。朱夫子以允文此言为得之矣。今世采亦无师承而与郑叔友相类。则先生之所以惜之者。岂不宜乎。
自知其分党之罪。同于逆律。只管务要突过先进而然也。先生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日之人。莫知有尊周之义者。诚可为寒心。故欲明我 太祖回军之义。使今人昭知有尊周之义矣。若非今日。则吾何必强要此事于 朝耶。朴和叔即不易得之人也。乃敢于此极力立异。而以没其尊周大义于今日。岂不惜哉。厥后上疏有曰。奉 上徽号于君父。乃臣子不能自已之义也。吾以为此人今方觉悟云。而窃喜于心矣。俄而复曰。臣子不可 上徽号之义。亦在其中云。何其语焉而不详者。至于斯耶。仍厉声曰。不言不可上。而乃曰。其中亦有不可上之意者。不亦怪乎。在渠不可上之意。人何以知之耶。盖先生虽不以此而显绝之矣。然鄙贱其不知尊周之义矣。又以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为甚轻之也。又以朴之防塞裁减之事。为有岐疾忌克之心而然也。以此观之。其与先生异者。朴无间于尹矣。而及先生之没也。世采敢有来附之意。至为之服云。因此而世采若有悔悟之心。著书自责。快示其改过之事于今日。则吾党之士。当与其自新之意而进之于吾党矣。今世采一无悔悟之语。又与尹拯交情益深。则渠虽为我先生而服也。孰信渠好名行诈之事乎。昔余允文辨斥郑叔友之言曰。专以偏见曲说而非诋孟子。学无师承。其弊也如此。卒为名教之罪人。惜哉。朱夫子以允文此言为得之矣。今世采亦无师承而与郑叔友相类。则先生之所以惜之者。岂不宜乎。甲子夏四月。慎在都下。得见尹拯答朴世采书。讥议先生以为有机关权数及不能无疑于本原言行等语。不胜骇愤。上章论辨矣。文谷老峰两相。乃因鄙疏而奏于 榻前。请勿以儒臣待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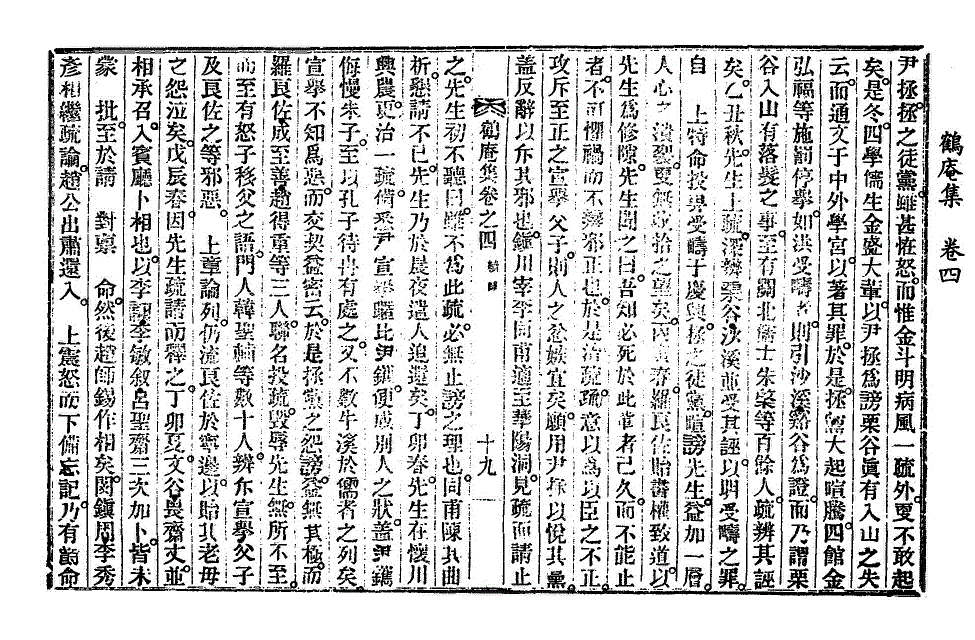 尹拯。拯之徒党。虽甚怪怒。而惟金斗明病风一疏外。更不敢起矣。是冬。四学儒生金盛大辈。以尹拯为谤栗谷真有入山之失云。而通文于中外学宫。以著其罪。于是。拯党大起喧腾。四馆金弘福等施罚停举。如洪受畴者。则引沙溪,溪谷为證。而乃谓栗谷入山有落发之事。至有关北儒士朱棨等百馀人。疏辨其诬矣。乙丑秋。先生上疏。深辨栗谷,沙溪并受其诬。以明受畴之罪。自 上特命投畀受畴于庆兴。拯之徒党。暄谤先生。益加一层。人心之溃裂。更无收拾之望矣。丙寅春。罗良佐贻书权致道。以先生为修隙。先生闻之曰。吾知必死于此辈者已久。而不能止者。不可惧祸而不辨邪正也。于是治疏。疏意以为以臣之不正。攻斥至正之宣举父子。则人之忿嫉宜矣。愿用尹拯以悦其党。盖反辞以斥其邪也。镇川宰李同甫适至华阳洞。见疏而请止之。先生初不听曰。虽不为此疏。必无止谤之理也。同甫陈其曲析。恳请不已。先生乃于晨夜遣人追还矣。丁卯春。先生在怀川兴农。更治一疏。备悉尹宣举昵比尹镌。便成别人之状。盖尹镌侮慢朱子。至以孔子待冉有处之。又不数牛溪于儒者之列矣。宣举不知为恶。而交契益密云。于是拯党之怨谤。益无其极。而罗良佐,成至善,赵得重等三人。联名投疏。毁辱先生。无所不至。而至有怒子移父之语。门人韩圣辅等数十人。辨斥岂举父子及良佐之等邪恶。 上章论列。仍流良佐于宁边。以贻其老母之怨泣矣。戊辰春。因先生疏请而释之。丁卯夏。文谷,畏斋丈。并相承召。入宾厅卜相也。以李䎘,李敏叙,吕圣斋三次加卜。皆未蒙 批。至于请 对禀 命。然后赵师锡作相矣。闵镇周,李秀彦相继疏论。赵公出肃还入。 上震怒而下备忘记。乃有爵命
尹拯。拯之徒党。虽甚怪怒。而惟金斗明病风一疏外。更不敢起矣。是冬。四学儒生金盛大辈。以尹拯为谤栗谷真有入山之失云。而通文于中外学宫。以著其罪。于是。拯党大起喧腾。四馆金弘福等施罚停举。如洪受畴者。则引沙溪,溪谷为證。而乃谓栗谷入山有落发之事。至有关北儒士朱棨等百馀人。疏辨其诬矣。乙丑秋。先生上疏。深辨栗谷,沙溪并受其诬。以明受畴之罪。自 上特命投畀受畴于庆兴。拯之徒党。暄谤先生。益加一层。人心之溃裂。更无收拾之望矣。丙寅春。罗良佐贻书权致道。以先生为修隙。先生闻之曰。吾知必死于此辈者已久。而不能止者。不可惧祸而不辨邪正也。于是治疏。疏意以为以臣之不正。攻斥至正之宣举父子。则人之忿嫉宜矣。愿用尹拯以悦其党。盖反辞以斥其邪也。镇川宰李同甫适至华阳洞。见疏而请止之。先生初不听曰。虽不为此疏。必无止谤之理也。同甫陈其曲析。恳请不已。先生乃于晨夜遣人追还矣。丁卯春。先生在怀川兴农。更治一疏。备悉尹宣举昵比尹镌。便成别人之状。盖尹镌侮慢朱子。至以孔子待冉有处之。又不数牛溪于儒者之列矣。宣举不知为恶。而交契益密云。于是拯党之怨谤。益无其极。而罗良佐,成至善,赵得重等三人。联名投疏。毁辱先生。无所不至。而至有怒子移父之语。门人韩圣辅等数十人。辨斥岂举父子及良佐之等邪恶。 上章论列。仍流良佐于宁边。以贻其老母之怨泣矣。戊辰春。因先生疏请而释之。丁卯夏。文谷,畏斋丈。并相承召。入宾厅卜相也。以李䎘,李敏叙,吕圣斋三次加卜。皆未蒙 批。至于请 对禀 命。然后赵师锡作相矣。闵镇周,李秀彦相继疏论。赵公出肃还入。 上震怒而下备忘记。乃有爵命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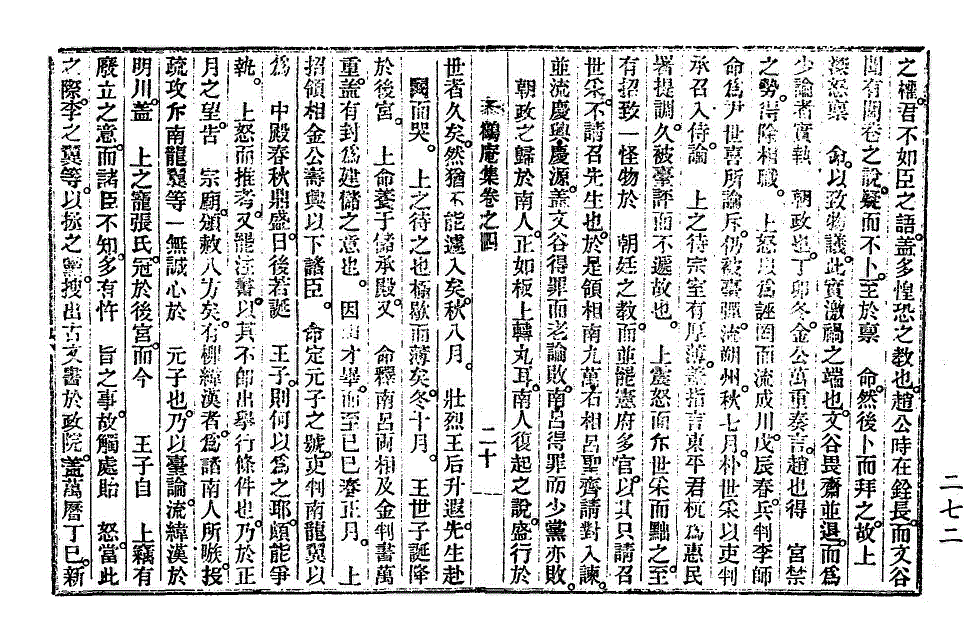 之权。君不如臣之语。盖多惶恐之教也。赵公时在铨长。而文谷闻有闾巷之说。疑而不卜。至于禀 命。然后卜而拜之。故上 深怒禀 命。以致物议。此实激祸之端也。文谷,畏斋并退。而为少论者实执 朝政也。丁卯冬。金公万重奏言。赵也得 宫禁之势。得除相职。 上怒以为诬罔而流成川。戊辰春。兵判李师命为尹世喜所论斥。仍被台弹。流朔州。秋七月。朴世采以吏判承召入侍。论 上之待宗室有厚薄。盖指言东平君杭为惠民署提调。久被台评而不递故也。 上震怒而斥世采而黜之。至有招致一怪物于 朝廷之教。而并罢宪府多官。以其只请召世采。不请召先生也。于是领相南九万,右相吕圣齐请对入谏。并流庆兴,庆源。盖文谷得罪而老论败。南,吕得罪而少党亦败。 朝政之归于南人。正如板上转丸耳。南人复起之说。盛行于世者久矣。然犹不能遽入矣。秋八月。 壮烈王后升遐。先生赴阙而哭。 上之待之也极歇而薄矣。冬十月。世子诞降于后宫。上命养于储承殿。又 命释南,吕两相及金判书万重。盖有封为建储之意也。 因山才毕。而至己巳春正月。 上招领相金公寿兴以下诸臣。 命定元子之号。吏判南龙翼以为耶。 中殿春秋鼎盛。日后若诞 王子。则何以为之耶颇能争执。 上怒而推考。又罢注书。以其不即出举行条件也。乃于正月之望。告 宗庙。颁赦八方矣。有柳纬汉者。为诸南人所嗾。投疏攻斥南龙翼等一无诚心于 元子也。乃以台论。流纬汉于明川。盖 上之宠张氏。冠于后宫。而今 王子自 上窃有废立之意。而诸臣不知。多有忤 旨之事。故触处贻 怒。当此之际。李之翼等。以拯之党。搜出古文书于政院。盖万历丁巳。新
之权。君不如臣之语。盖多惶恐之教也。赵公时在铨长。而文谷闻有闾巷之说。疑而不卜。至于禀 命。然后卜而拜之。故上 深怒禀 命。以致物议。此实激祸之端也。文谷,畏斋并退。而为少论者实执 朝政也。丁卯冬。金公万重奏言。赵也得 宫禁之势。得除相职。 上怒以为诬罔而流成川。戊辰春。兵判李师命为尹世喜所论斥。仍被台弹。流朔州。秋七月。朴世采以吏判承召入侍。论 上之待宗室有厚薄。盖指言东平君杭为惠民署提调。久被台评而不递故也。 上震怒而斥世采而黜之。至有招致一怪物于 朝廷之教。而并罢宪府多官。以其只请召世采。不请召先生也。于是领相南九万,右相吕圣齐请对入谏。并流庆兴,庆源。盖文谷得罪而老论败。南,吕得罪而少党亦败。 朝政之归于南人。正如板上转丸耳。南人复起之说。盛行于世者久矣。然犹不能遽入矣。秋八月。 壮烈王后升遐。先生赴阙而哭。 上之待之也极歇而薄矣。冬十月。世子诞降于后宫。上命养于储承殿。又 命释南,吕两相及金判书万重。盖有封为建储之意也。 因山才毕。而至己巳春正月。 上招领相金公寿兴以下诸臣。 命定元子之号。吏判南龙翼以为耶。 中殿春秋鼎盛。日后若诞 王子。则何以为之耶颇能争执。 上怒而推考。又罢注书。以其不即出举行条件也。乃于正月之望。告 宗庙。颁赦八方矣。有柳纬汉者。为诸南人所嗾。投疏攻斥南龙翼等一无诚心于 元子也。乃以台论。流纬汉于明川。盖 上之宠张氏。冠于后宫。而今 王子自 上窃有废立之意。而诸臣不知。多有忤 旨之事。故触处贻 怒。当此之际。李之翼等。以拯之党。搜出古文书于政院。盖万历丁巳。新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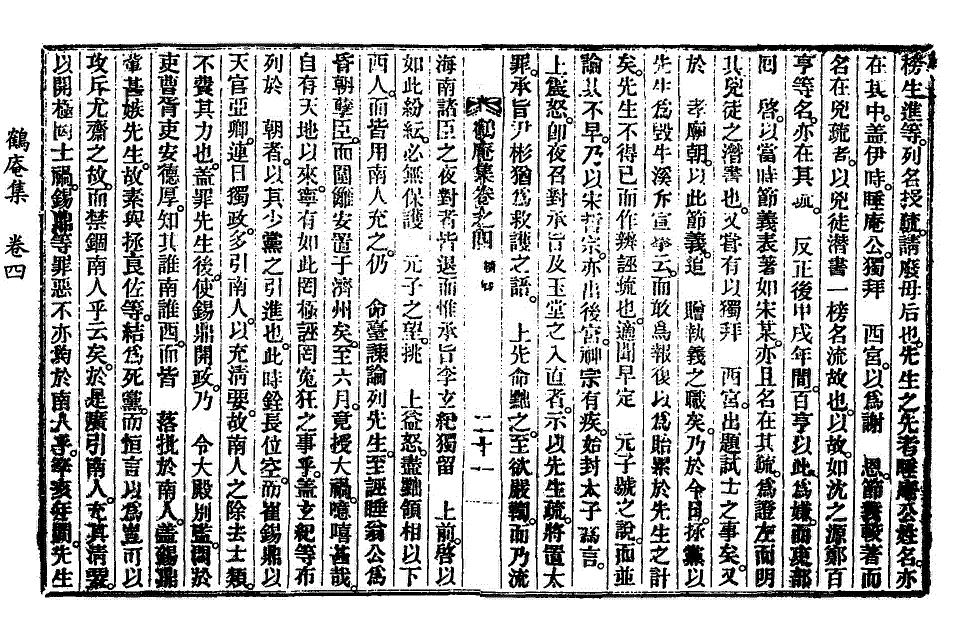 榜生进等。列名投疏。请废母后也。先生之先考睡庵公姓名。亦在其中。盖伊时。睡庵公。独拜 西宫。以为谢 恩。节义较著而名在凶疏者。以凶徒潜书一榜名流故也。以故。如沈之源郑百亨等名。亦在其疏。 反正后甲戌年间。百亨以此为嫌。而吏部回 启。以当时节义表著如宋某。亦且名在其疏。为證左而明其凶徒之潜书也。又尝有以独拜 西宫。出题试士之事矣。又于 孝庙朝。以此节义。追 赠执义之职矣。乃于今日。拯党以先生为毁牛溪斥宣举云。而敢为报复以为贻累于先生之计矣。先生不得已而作辨诬疏也。适闻早定 元子号之说。而并论其不早。乃以宋哲宗。亦出后宫。神宗有疾。始封太子为言。 上震怒。即夜召对承旨及玉堂之入直者。示以先生疏。将置太罪。承旨尹彬犹为救护之语。 上先命黜之。至欲严鞫。而乃流海南诸臣之夜对者皆退而惟承旨李玄纪独留 上前。启以如此纷纭。必无保护 元子之望。挑 上益怒。尽黜领相以下西人。而皆用南人充之。仍 命台谏论列先生。至诬睡翁公为昏朝孽臣。而围篱安置于济州矣。至六月。竟授大祸。噫嘻甚哉。自有天地以来。宁有如此罔极诬罔冤狂之事乎。盖玄纪等布列于 朝者。以其少党之引进也。此时铨长位空。而崔锡鼎以天官亚卿。连日独政。多引南人。以充清要。故南人之除去士类。不费其力也。盖罪先生后。使锡鼎开政。乃 令大殿别监。问于吏曹胥吏安德厚。知其谁南谁西。而皆 落批于南人。盖锡鼎辈甚嫉先生。故素与拯良佐等。结为死党。而恒言以为岂可以攻斥尤斋之故。而禁锢南人乎云矣。于是广引南人。充其清要以开极罔士祸。锡鼎等罪恶不亦均于南人乎。辛亥年间。先生
榜生进等。列名投疏。请废母后也。先生之先考睡庵公姓名。亦在其中。盖伊时。睡庵公。独拜 西宫。以为谢 恩。节义较著而名在凶疏者。以凶徒潜书一榜名流故也。以故。如沈之源郑百亨等名。亦在其疏。 反正后甲戌年间。百亨以此为嫌。而吏部回 启。以当时节义表著如宋某。亦且名在其疏。为證左而明其凶徒之潜书也。又尝有以独拜 西宫。出题试士之事矣。又于 孝庙朝。以此节义。追 赠执义之职矣。乃于今日。拯党以先生为毁牛溪斥宣举云。而敢为报复以为贻累于先生之计矣。先生不得已而作辨诬疏也。适闻早定 元子号之说。而并论其不早。乃以宋哲宗。亦出后宫。神宗有疾。始封太子为言。 上震怒。即夜召对承旨及玉堂之入直者。示以先生疏。将置太罪。承旨尹彬犹为救护之语。 上先命黜之。至欲严鞫。而乃流海南诸臣之夜对者皆退而惟承旨李玄纪独留 上前。启以如此纷纭。必无保护 元子之望。挑 上益怒。尽黜领相以下西人。而皆用南人充之。仍 命台谏论列先生。至诬睡翁公为昏朝孽臣。而围篱安置于济州矣。至六月。竟授大祸。噫嘻甚哉。自有天地以来。宁有如此罔极诬罔冤狂之事乎。盖玄纪等布列于 朝者。以其少党之引进也。此时铨长位空。而崔锡鼎以天官亚卿。连日独政。多引南人。以充清要。故南人之除去士类。不费其力也。盖罪先生后。使锡鼎开政。乃 令大殿别监。问于吏曹胥吏安德厚。知其谁南谁西。而皆 落批于南人。盖锡鼎辈甚嫉先生。故素与拯良佐等。结为死党。而恒言以为岂可以攻斥尤斋之故。而禁锢南人乎云矣。于是广引南人。充其清要以开极罔士祸。锡鼎等罪恶不亦均于南人乎。辛亥年间。先生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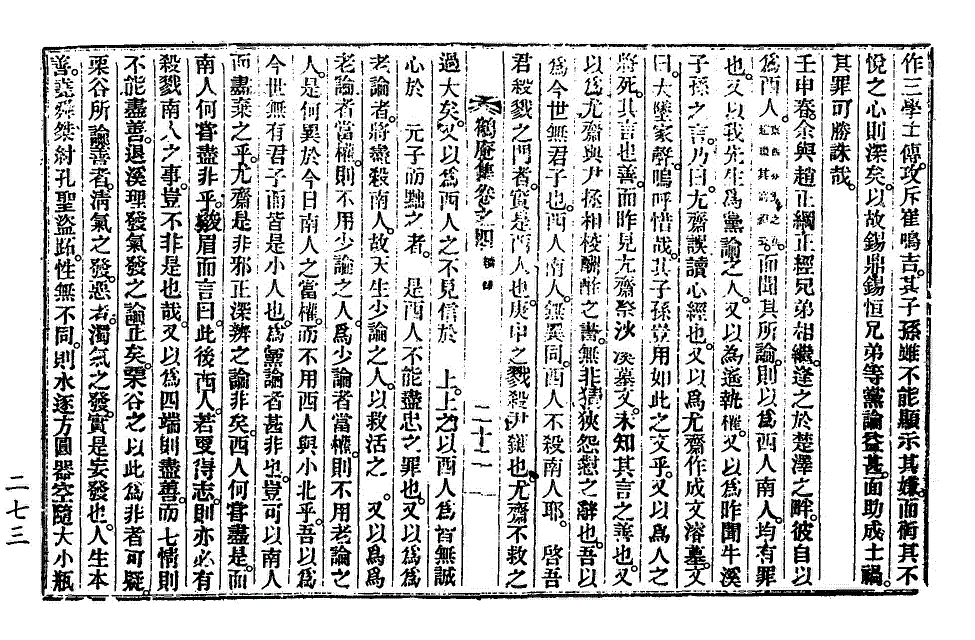 作三学士传。攻斥崔鸣吉。其子孙虽不能显示其嫌。而衔其不悦之心则深矣。以故锡鼎,锡恒兄弟等党论益甚。面助成士祸。其罪可胜诛哉。
作三学士传。攻斥崔鸣吉。其子孙虽不能显示其嫌。而衔其不悦之心则深矣。以故锡鼎,锡恒兄弟等党论益甚。面助成士祸。其罪可胜诛哉。壬申春。余与赵正纲正经兄弟相继。逢之于楚泽之畔。彼自以为西人。(东西分党之初。赵琼其高祖云。)而闻其所论。则以为西人南人。均有罪也。又以我先生为党论之人。又以为遥执权。又以为昨闻牛溪子孙之言。乃曰。尤斋误读心经也。又以为尤斋作成文浚墓。文曰。大坠家声。呜呼惜哉。其子孙岂用如此之文乎。又以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昨见尤斋祭沙溪墓文。未知其言之善也。又以为尤斋与尹拯相校酬酢之书。无非猜狭怨怼之辞也。吾以为今世无君子也。西人南人。无异同。西人不杀南人耶。 启吾君杀戮之门者。实是西人也。庚申之戮杀尹镌也。尤斋不救之过大矣。又以为西人之不见信于 上。上之以西人为皆无诚心于 元子而黜之者。 是西人不能尽忠之罪也。又以为为老论者。将尽杀南人。故天生少论之人。以救活之 。又以为为老论者当权。则不用少论之人。为少论者当权。则不用老论之人。是何异于今日南人之当权。而不用西人与小北乎。吾以为今世无有君子而皆是小人也。为党论者甚非也。岂可以南人而尽弃之乎。尤斋是非邪正深辨之论非矣。西人何尝尽是。而南人何尝尽非乎。▦眉而言曰。此后西人。若更得志。则亦必有杀戮南人之事。岂不非是也哉。又以为四端则尽善。而七情则不能尽善。退溪理发气发之论正矣。栗谷之以此为非者可疑。栗谷所论善者。清气之发。恶者。浊气之发。实是妄发也。人生本善。尧舜桀纣孔圣盗蹠。性无不同。则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
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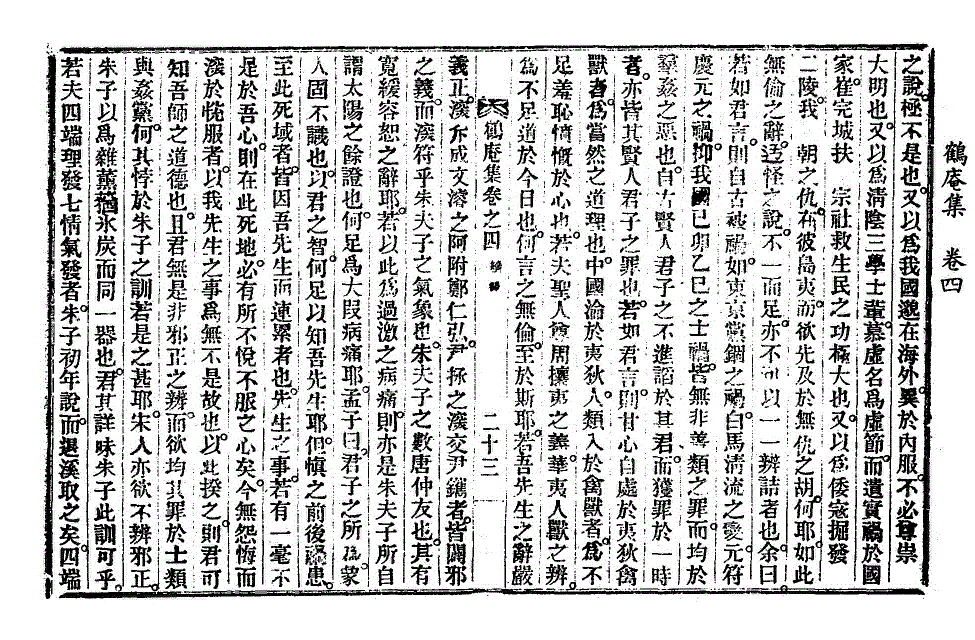 之说。极不是也。又以为我国邈在海外。异于内服。不必尊崇 大明也。又以为清阴三学士辈。慕虚名为虚节。而遗实祸于国家。崔完城扶 宗社救生民之功极大也。又以为倭寇掘发 二陵。我 朝之仇。在彼岛夷。而欲先及于无仇之胡。何耶。如此无伦之辞。迂怪之说。不一而足。亦不可以一一辨诘者也。余曰。若如君言。则自古被祸。如东京党锢之祸。白马清流之变。元符庆元之祸。抑我国己卯乙巳之士祸。皆无非善类之罪。而均于群奸之恶也。自古贤人君子之不进谄于其君。而获罪于一时者。亦皆其贤人君子之罪也。若如君言。则甘心自处于夷狄禽兽者。为当然之道理也。中国沦于夷狄。人类入于禽兽者。为不足羞耻愤慨于心也。若夫圣人尊周攘夷之义。华夷人兽之辨。为不足道于今日也。何言之无伦。至于斯耶。若吾先生之辞严义正。深斥成文浚之阿附郑仁弘。尹拯之深交尹镌者。皆辟邪之义。而深符乎朱夫子之气象也。朱夫子之数唐仲友也。其有宽缓容恕之辞耶。若以此为过激之病痛。则亦是朱夫子所自谓太阳之馀證也。何足为大段病痛耶。孟子曰。君子之所为。象(一作众)人固不识也。以君之智。何足以知吾先生耶。但慎之前后祸患。至此死域者。皆因吾先生而连累者也。先生之事。若有一毫不是于吾心。则在此死地。必有所不悦不服之心矣。今无怨悔而深于悦服者。以我先生之事为无不是故也。以此揆之。则君可知吾师之道德也。且君无是非邪正之辨。而欲均其罪于士类与奸党。何其悖于朱子之训若是之甚耶。宋人亦欲不辨邪正。朱子以为杂薰莸冰炭而同一器也。君其详味朱子此训可乎。若夫四端理发七情气发者。朱子初年说。而退溪取之矣。四端
之说。极不是也。又以为我国邈在海外。异于内服。不必尊崇 大明也。又以为清阴三学士辈。慕虚名为虚节。而遗实祸于国家。崔完城扶 宗社救生民之功极大也。又以为倭寇掘发 二陵。我 朝之仇。在彼岛夷。而欲先及于无仇之胡。何耶。如此无伦之辞。迂怪之说。不一而足。亦不可以一一辨诘者也。余曰。若如君言。则自古被祸。如东京党锢之祸。白马清流之变。元符庆元之祸。抑我国己卯乙巳之士祸。皆无非善类之罪。而均于群奸之恶也。自古贤人君子之不进谄于其君。而获罪于一时者。亦皆其贤人君子之罪也。若如君言。则甘心自处于夷狄禽兽者。为当然之道理也。中国沦于夷狄。人类入于禽兽者。为不足羞耻愤慨于心也。若夫圣人尊周攘夷之义。华夷人兽之辨。为不足道于今日也。何言之无伦。至于斯耶。若吾先生之辞严义正。深斥成文浚之阿附郑仁弘。尹拯之深交尹镌者。皆辟邪之义。而深符乎朱夫子之气象也。朱夫子之数唐仲友也。其有宽缓容恕之辞耶。若以此为过激之病痛。则亦是朱夫子所自谓太阳之馀證也。何足为大段病痛耶。孟子曰。君子之所为。象(一作众)人固不识也。以君之智。何足以知吾先生耶。但慎之前后祸患。至此死域者。皆因吾先生而连累者也。先生之事。若有一毫不是于吾心。则在此死地。必有所不悦不服之心矣。今无怨悔而深于悦服者。以我先生之事为无不是故也。以此揆之。则君可知吾师之道德也。且君无是非邪正之辨。而欲均其罪于士类与奸党。何其悖于朱子之训若是之甚耶。宋人亦欲不辨邪正。朱子以为杂薰莸冰炭而同一器也。君其详味朱子此训可乎。若夫四端理发七情气发者。朱子初年说。而退溪取之矣。四端鹤庵集卷之四 第 274L 页
 亦有以不正而发者。则不可专以为理发者。亦朱子后来说。而栗谷取之。以正其理发之未稳者。极当无疑矣。如梁武帝不忍断死刑。亦可谓恻隐之心。而不正甚矣。则岂可谓此为理发乎。且禀得天地之元气者为圣人。禀得纯粹之气者为大贤。禀得昏浊之气者为下愚。此栗谷所以取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之说。而乃有清气浊气之语耳。论性而不论气。则为不备矣。性虽至善。堕于形气。则有万不同。不能致其克治之工。则桀纣必不得为尧舜矣。盗蹠乌能至于孔子乎。故朱子以为极难也。盖朱子出于南宋。然后虽周,程,张子之说。有不可从者也。栗谷兴于吾东。则吾东大贤之言。亦有所不可从者多矣。今君反栗谷之言为理发。君可谓自陷于妄发。而不见其眉睫也。如是攻辨者多矣。而赵之兄弟坚白不屈。盖其外祖即金佐明也。暨厥父兄毁谤我先生之说。习于耳。今日尹党诋斥我先生之状。熟于目。故年少气锐。主其先入。而亦不自知其陷于邪诐之行。实甚可哀。而为不足辨也。然其自先世所论若是其痴呆可笑。而渠之兄弟年皆甚少。亦皆达象也。若或得志于方来。则其害必不止于洪水猛兽。故闲并录之。以俟夫知言之君子。明辨之正士云。
亦有以不正而发者。则不可专以为理发者。亦朱子后来说。而栗谷取之。以正其理发之未稳者。极当无疑矣。如梁武帝不忍断死刑。亦可谓恻隐之心。而不正甚矣。则岂可谓此为理发乎。且禀得天地之元气者为圣人。禀得纯粹之气者为大贤。禀得昏浊之气者为下愚。此栗谷所以取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之说。而乃有清气浊气之语耳。论性而不论气。则为不备矣。性虽至善。堕于形气。则有万不同。不能致其克治之工。则桀纣必不得为尧舜矣。盗蹠乌能至于孔子乎。故朱子以为极难也。盖朱子出于南宋。然后虽周,程,张子之说。有不可从者也。栗谷兴于吾东。则吾东大贤之言。亦有所不可从者多矣。今君反栗谷之言为理发。君可谓自陷于妄发。而不见其眉睫也。如是攻辨者多矣。而赵之兄弟坚白不屈。盖其外祖即金佐明也。暨厥父兄毁谤我先生之说。习于耳。今日尹党诋斥我先生之状。熟于目。故年少气锐。主其先入。而亦不自知其陷于邪诐之行。实甚可哀。而为不足辨也。然其自先世所论若是其痴呆可笑。而渠之兄弟年皆甚少。亦皆达象也。若或得志于方来。则其害必不止于洪水猛兽。故闲并录之。以俟夫知言之君子。明辨之正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