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x 页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书(七首)
书(七首)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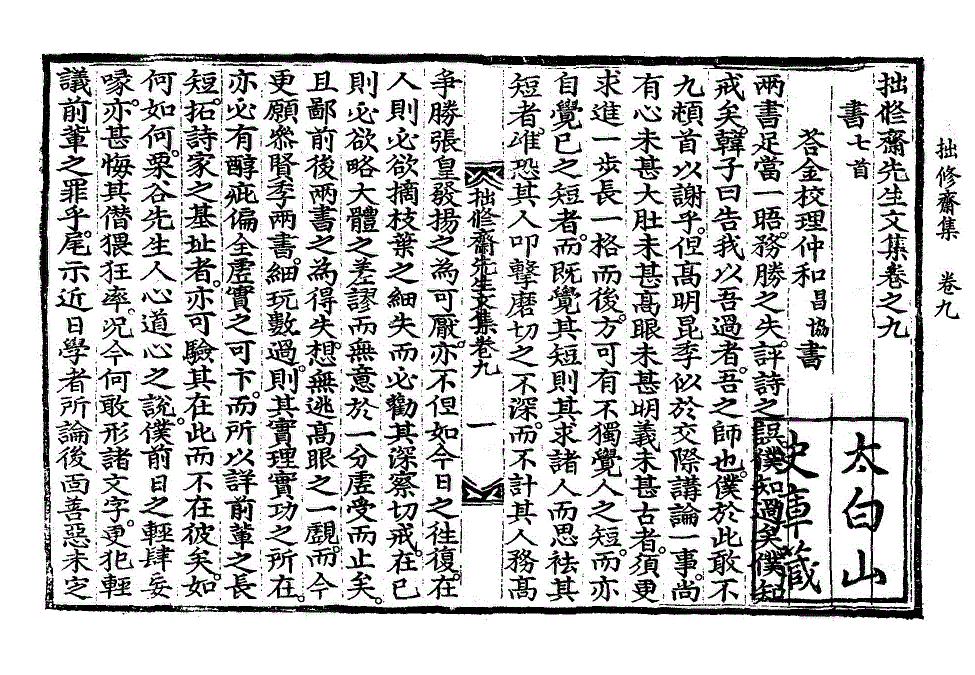 答金校理仲和(昌协)书
答金校理仲和(昌协)书两书足当一晤。务胜之失。评诗之误。仆知过矣。仆知戒矣。韩子曰告我以吾过者。吾之师也。仆于此敢不九顿首以谢乎。但高明昆季似于交际讲论一事。尚有心未甚大肚未甚高眼未甚明义未甚古者。须更求进一步长一格而后。方可有不独觉人之短。而亦自觉己之短者。而既觉其短则其求诸人而思袪其短者。唯恐其人叩击磨切之不深。而不计其人务高争胜张皇发扬之为可厌。亦不但如今日之往复。在人则必欲摘枝叶之细失而必劝其深察切戒。在己则必欲略大体之差谬而无意于一分虚受而止矣。且鄙前后两书之为得失。想无逃高眼之一觑。而今更愿参贤季两书。细玩数过。则其实理实功之所在。亦必有醇疵偏全虚实之可卞。而所以详前辈之长短。拓诗家之基址者。亦可验其在此而不在彼矣。如何如何。栗谷先生人心道心之说。仆前日之轻肆妄喙。亦甚悔其僭猥狂率。况今何敢形诸文字。更犯轻议前辈之罪乎。尾示近日学者所论后面善恶未定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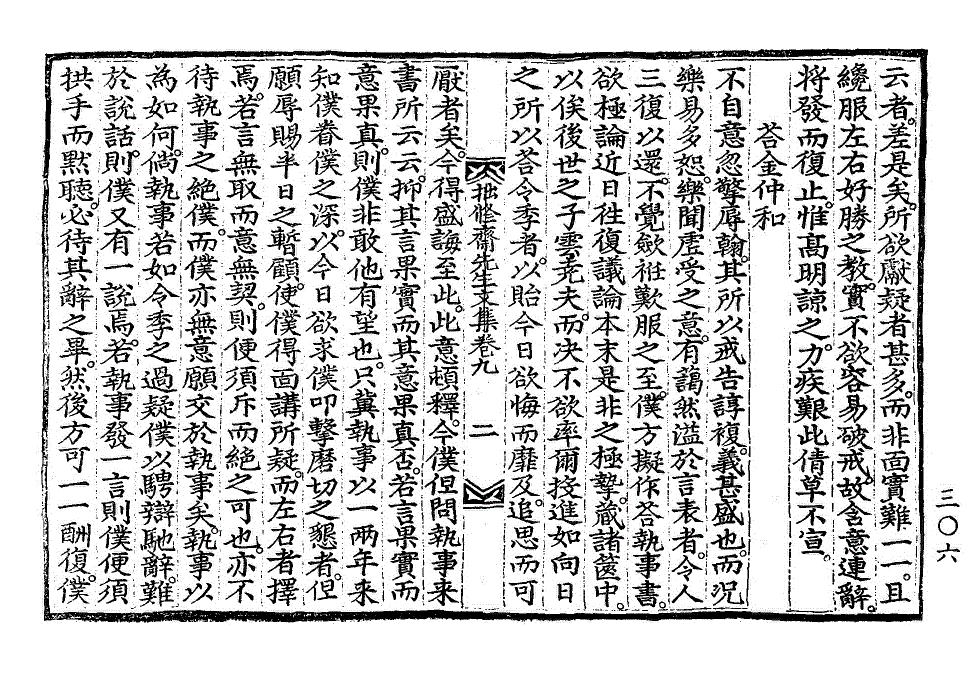 云者。差是矣。所欲献疑者甚多。而非面实难一一。且才服左右好胜之教。实不欲容易破戒。故含意连辞。将发而复止。惟高明谅之。力疾艰此倩草不宣。
云者。差是矣。所欲献疑者甚多。而非面实难一一。且才服左右好胜之教。实不欲容易破戒。故含意连辞。将发而复止。惟高明谅之。力疾艰此倩草不宣。答金仲和
不自意忽擎辱翰。其所以戒告谆复。义甚盛也。而况乐易多恕。乐闻虚受之意。有蔼然溢于言表者。令人三复以还。不觉敛衽叹服之至。仆方拟作答执事书。欲极论近日往复议论本末是非之极挚。藏诸箧中。以俟后世之子云,尧夫。而决不欲率尔投进如向日之所以答令季者。以贻今日欲悔而靡及。追思而可厌者矣。今得盛诲至此。此意顿释。今仆但问执事来书所云云。抑其言果实而其意果真否。若言果实而意果真。则仆非敢他有望也。只冀执事以一两年来知仆眷仆之深。以今日欲求仆叩击磨切之恳者。但愿辱赐半日之暂顾。使仆得面讲所疑。而左右者择焉。若言无取而意无契。则便须斥而绝之可也。亦不待执事之绝仆。而仆亦无意愿交于执事矣。执事以为如何。倘执事若如令季之过疑仆以骋辩驰辞。难于说话。则仆又有一说焉。若执事发一言则仆便须拱手而默听。必待其辞之毕。然后方可一一酬复。仆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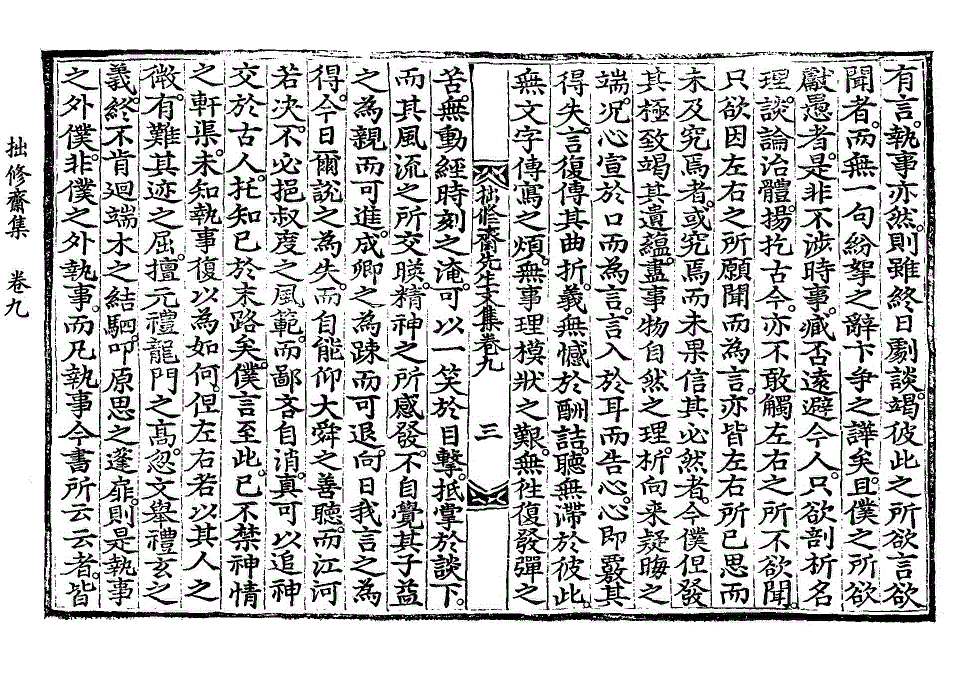 有言。执事亦然。则虽终日剧谈。竭彼此之所欲言欲闻者。而无一句纷挐之辞卞争之哗矣。且仆之所欲献愚者。是非不涉时事。臧否远避今人。只欲剖析名理。谈论治体。扬扢古今。亦不敢触左右之所不欲闻。只欲因左右之所愿闻而为言。亦皆左右所已思而未及究焉者。或究焉而未果信其必然者。今仆但发其极致竭其遗蕴。尽事物自然之理。析向来疑晦之端。况心宣于口而为言。言入于耳而告心。心即覈其得失。言复传其曲折。义无憾于酬诘。听无滞于彼此。无文字传写之烦。无事理模状之艰。无往复发弹之苦。无动经时刻之淹。可以一笑于目击。抵掌于谈下。而其风流之所交映。精神之所感发。不自觉其子益之为亲而可进。成卿之为疏而可退。向日我言之为得。今日尔说之为失。而自能仰大舜之善听。而江河若决。不必挹叔度之风范。而鄙吝自消。真可以追神交于古人。托知己于末路矣。仆言至此。已不禁神情之轩渠。未知执事复以为如何。但左右若以其人之微。有难其迹之屈。擅元礼龙门之高。忽文举礼玄之义。终不肯回端木之结驷。叩原思之蓬扉。则是执事之外仆。非仆之外执事。而凡执事今书所云云者。皆
有言。执事亦然。则虽终日剧谈。竭彼此之所欲言欲闻者。而无一句纷挐之辞卞争之哗矣。且仆之所欲献愚者。是非不涉时事。臧否远避今人。只欲剖析名理。谈论治体。扬扢古今。亦不敢触左右之所不欲闻。只欲因左右之所愿闻而为言。亦皆左右所已思而未及究焉者。或究焉而未果信其必然者。今仆但发其极致竭其遗蕴。尽事物自然之理。析向来疑晦之端。况心宣于口而为言。言入于耳而告心。心即覈其得失。言复传其曲折。义无憾于酬诘。听无滞于彼此。无文字传写之烦。无事理模状之艰。无往复发弹之苦。无动经时刻之淹。可以一笑于目击。抵掌于谈下。而其风流之所交映。精神之所感发。不自觉其子益之为亲而可进。成卿之为疏而可退。向日我言之为得。今日尔说之为失。而自能仰大舜之善听。而江河若决。不必挹叔度之风范。而鄙吝自消。真可以追神交于古人。托知己于末路矣。仆言至此。已不禁神情之轩渠。未知执事复以为如何。但左右若以其人之微。有难其迹之屈。擅元礼龙门之高。忽文举礼玄之义。终不肯回端木之结驷。叩原思之蓬扉。则是执事之外仆。非仆之外执事。而凡执事今书所云云者。皆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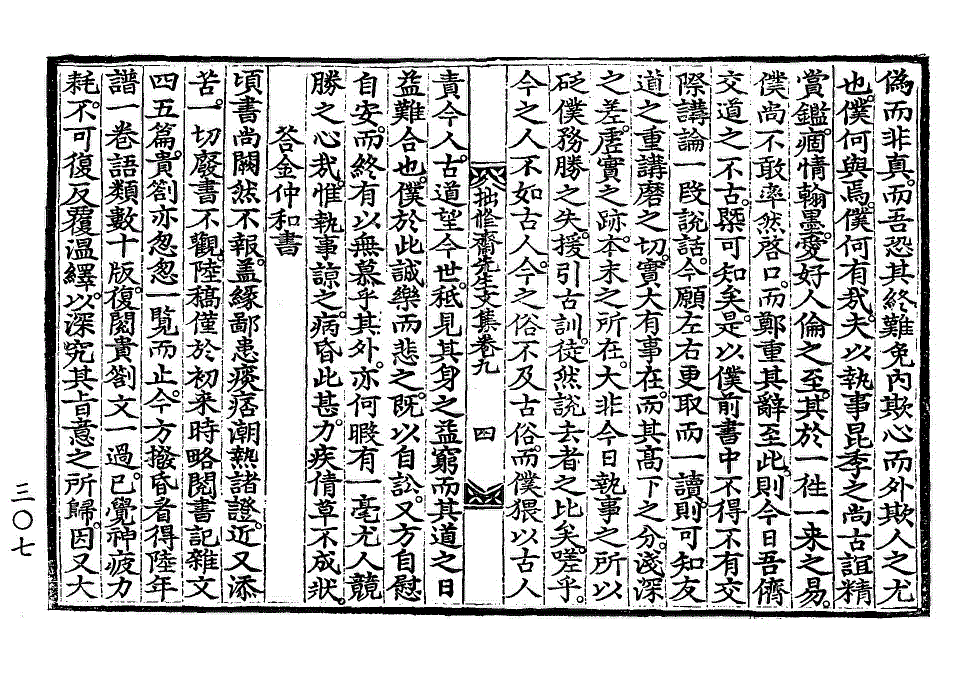 伪而非真。而吾恐其终难免内欺心而外欺人之尤也。仆何与焉。仆何有哉。夫以执事昆季之尚古谊精赏鉴。痼情翰墨。爱好人伦之至。其于一往一来之易。仆尚不敢率然启口。而郑重其辞至此。则今日吾侪交道之不古。槩可知矣。是以仆前书中不得不有交际讲论一段说话。今愿左右更取而一读。则可知友道之重讲磨之切。实大有事在。而其高下之分。浅深之差。虚实之迹。本末之所在。大非今日执事之所以砭仆务胜之失。援引古训。徒然说去者之比矣。嗟乎。今之人不如古人。今之俗不及古俗。而仆猥以古人责今人。古道望今世。秪见其身之益穷而其道之日益难合也。仆于此诚乐而悲之。既以自讼。又方自慰自安。而终有以无慕乎其外。亦何暇有一毫尤人竞胜之心哉。惟执事谅之。病昏此甚。力疾倩草不成状。
伪而非真。而吾恐其终难免内欺心而外欺人之尤也。仆何与焉。仆何有哉。夫以执事昆季之尚古谊精赏鉴。痼情翰墨。爱好人伦之至。其于一往一来之易。仆尚不敢率然启口。而郑重其辞至此。则今日吾侪交道之不古。槩可知矣。是以仆前书中不得不有交际讲论一段说话。今愿左右更取而一读。则可知友道之重讲磨之切。实大有事在。而其高下之分。浅深之差。虚实之迹。本末之所在。大非今日执事之所以砭仆务胜之失。援引古训。徒然说去者之比矣。嗟乎。今之人不如古人。今之俗不及古俗。而仆猥以古人责今人。古道望今世。秪见其身之益穷而其道之日益难合也。仆于此诚乐而悲之。既以自讼。又方自慰自安。而终有以无慕乎其外。亦何暇有一毫尤人竞胜之心哉。惟执事谅之。病昏此甚。力疾倩草不成状。答金仲和书
顷书尚阙然不报。盖缘鄙患痰痞潮热诸證。近又添苦。一切废书不观。陆稿仅于初来时略阅书记杂文四五篇。贵劄亦悤悤一览而止。今方拨昏看得陆年谱一卷语类数十版。复阅贵劄文一过。已觉神疲力耗。不可复反覆温绎。以深究其旨意之所归。因又大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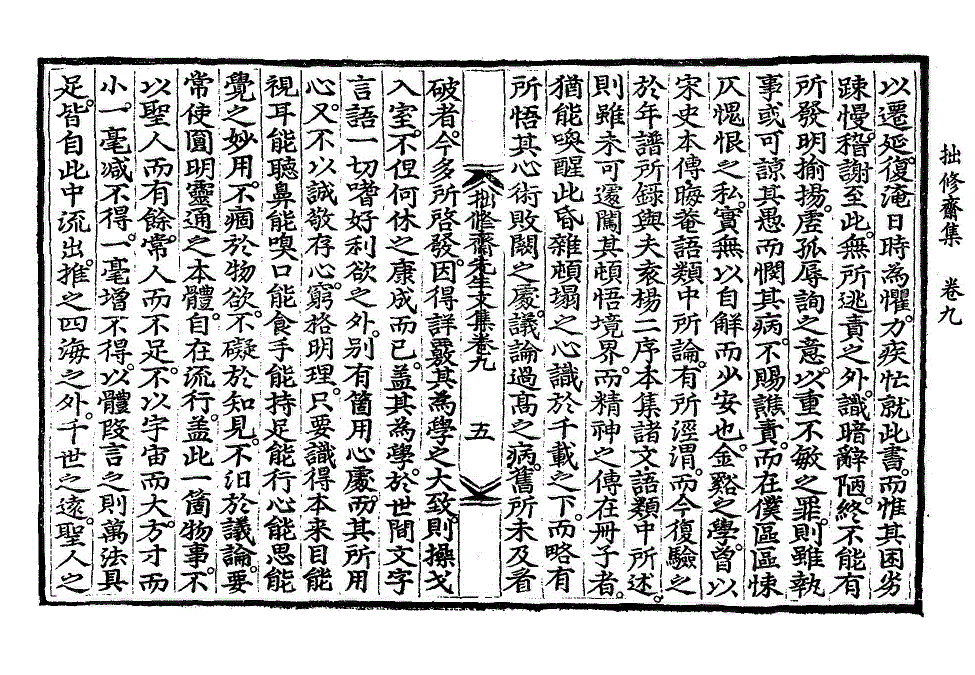 以迁延。复淹日时为惧。力疾忙就此书。而惟其困劣疏慢。稽谢至此。无所逃责之外。识暗辞陋。终不能有所发明揄扬。虚孤辱询之意。以重不敏之罪。则虽执事或可谅其愚而悯其病。不赐谯责。而在仆区区悚仄愧恨之私。实无以自解而少安也。金溪之学。曾以宋史本传,晦庵语类中所论。有所泾渭。而今复验之于年谱所录与夫袁杨二序,本集诸文,语类中所述。则虽未可遽闯其顿悟境界。而精神之传在册子者。犹能唤醒此昏杂顿塌之心识于千载之下。而略有所悟其心术败阙之处。议论过高之病。旧所未及看破者。今多所启发。因得详覈其为学之大致。则操戈入室。不但何休之康成而已。盖其为学。于世间文字言语一切嗜好利欲之外。别有个用心处。而其所用心。又不以诚敬存心。穷格明理。只要识得本来目能视耳能听鼻能嗅口能食手能持足能行心能思能觉之妙用。不痼于物欲。不碍于知见。不汩于议论。要常使圆明灵通之本体。自在流行。盖此一个物事。不以圣人而有馀。常人而不足。不以宇宙而大。方才而小。一毫减不得。一毫增不得。以体段言之则万法具足。皆自此中流出。推之四海之外。千世之远。圣人之
以迁延。复淹日时为惧。力疾忙就此书。而惟其困劣疏慢。稽谢至此。无所逃责之外。识暗辞陋。终不能有所发明揄扬。虚孤辱询之意。以重不敏之罪。则虽执事或可谅其愚而悯其病。不赐谯责。而在仆区区悚仄愧恨之私。实无以自解而少安也。金溪之学。曾以宋史本传,晦庵语类中所论。有所泾渭。而今复验之于年谱所录与夫袁杨二序,本集诸文,语类中所述。则虽未可遽闯其顿悟境界。而精神之传在册子者。犹能唤醒此昏杂顿塌之心识于千载之下。而略有所悟其心术败阙之处。议论过高之病。旧所未及看破者。今多所启发。因得详覈其为学之大致。则操戈入室。不但何休之康成而已。盖其为学。于世间文字言语一切嗜好利欲之外。别有个用心处。而其所用心。又不以诚敬存心。穷格明理。只要识得本来目能视耳能听鼻能嗅口能食手能持足能行心能思能觉之妙用。不痼于物欲。不碍于知见。不汩于议论。要常使圆明灵通之本体。自在流行。盖此一个物事。不以圣人而有馀。常人而不足。不以宇宙而大。方才而小。一毫减不得。一毫增不得。以体段言之则万法具足。皆自此中流出。推之四海之外。千世之远。圣人之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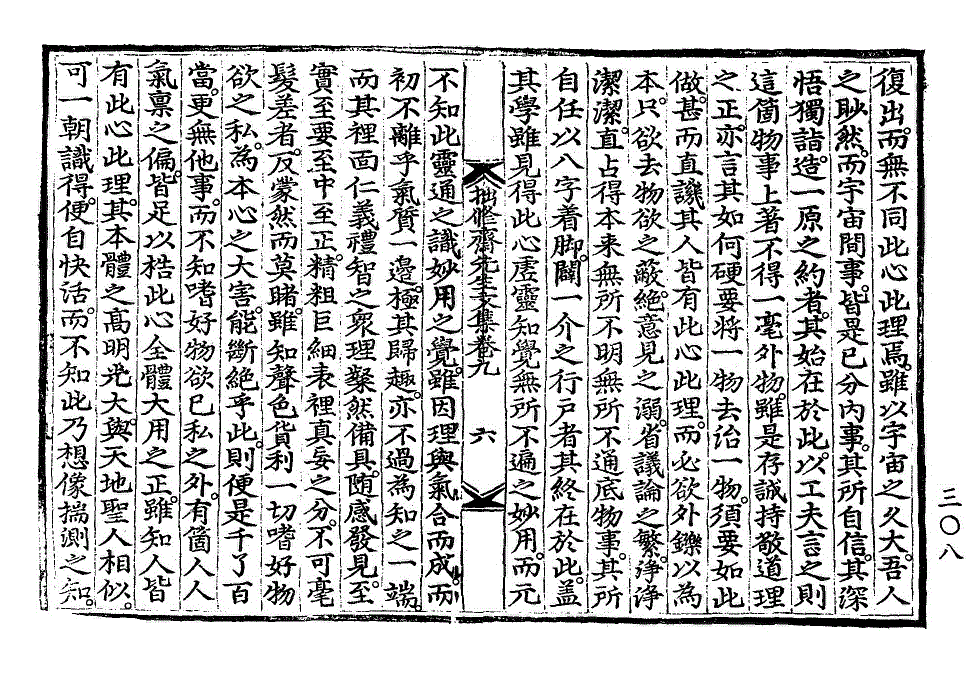 复出。而无不同此心此理焉。虽以宇宙之久大。吾人之眇然。而宇宙间事。皆是己分内事。其所自信。其深悟独诣。造一原之约者。其始在于此。以工夫言之则这个物事上著不得一毫外物。虽是存诚持敬道理之正。亦言其如何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须要如此做。甚而直讥其人皆有此心此理。而必欲外铄以为本。只欲去物欲之蔽。绝意见之溺。省议论之繁。净净洁洁。直占得本来无所不明无所不通底物事。其所自任以八字着脚。辟一介之行户者其终在于此。盖其学虽见得此心虚灵知觉无所不遍之妙用。而元不知此灵通之识妙用之觉。虽因理与气合而成。而初不离乎气质一边。极其归趣。亦不过为知之一端。而其里面仁义礼智之众理粲然备具。随感发见。至实至要至中至正。精粗巨细表里真妄之分。不可毫发差者。反蒙然而莫睹。虽知声色货利一切嗜好物欲之私。为本心之大害。能断绝乎此。则便是千了百当。更无他事。而不知嗜好物欲己私之外。有个人人气禀之偏。皆足以梏此心全体大用之正。虽知人皆有此心此理。其本体之高明光大。与天地圣人相似。可一朝识得。便自快活。而不知此乃想像揣测之知。
复出。而无不同此心此理焉。虽以宇宙之久大。吾人之眇然。而宇宙间事。皆是己分内事。其所自信。其深悟独诣。造一原之约者。其始在于此。以工夫言之则这个物事上著不得一毫外物。虽是存诚持敬道理之正。亦言其如何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须要如此做。甚而直讥其人皆有此心此理。而必欲外铄以为本。只欲去物欲之蔽。绝意见之溺。省议论之繁。净净洁洁。直占得本来无所不明无所不通底物事。其所自任以八字着脚。辟一介之行户者其终在于此。盖其学虽见得此心虚灵知觉无所不遍之妙用。而元不知此灵通之识妙用之觉。虽因理与气合而成。而初不离乎气质一边。极其归趣。亦不过为知之一端。而其里面仁义礼智之众理粲然备具。随感发见。至实至要至中至正。精粗巨细表里真妄之分。不可毫发差者。反蒙然而莫睹。虽知声色货利一切嗜好物欲之私。为本心之大害。能断绝乎此。则便是千了百当。更无他事。而不知嗜好物欲己私之外。有个人人气禀之偏。皆足以梏此心全体大用之正。虽知人皆有此心此理。其本体之高明光大。与天地圣人相似。可一朝识得。便自快活。而不知此乃想像揣测之知。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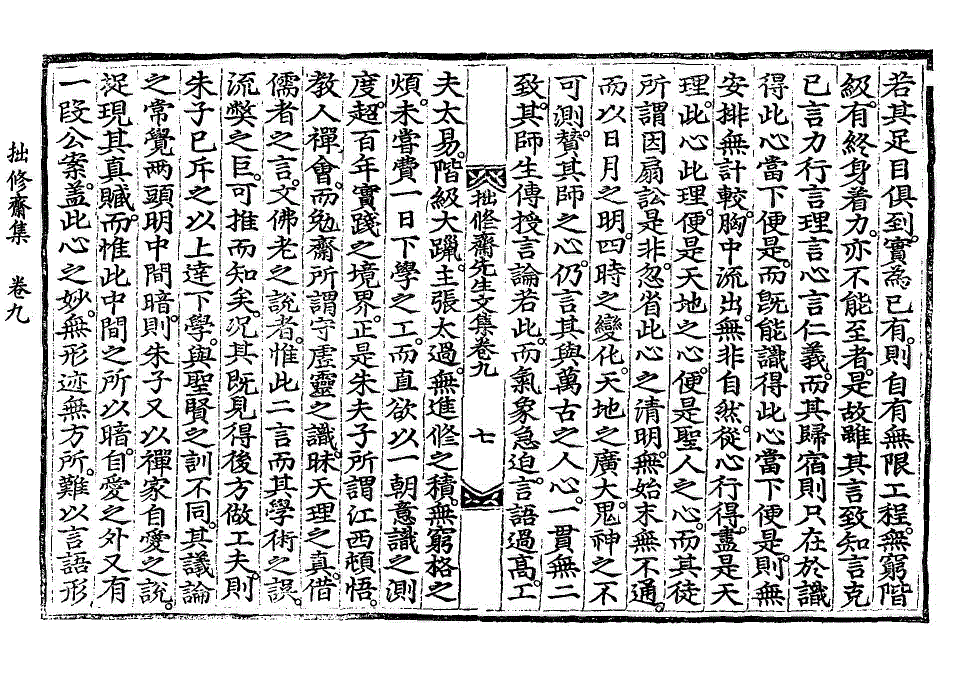 若其足目俱到。实为己有。则自有无限工程。无穷阶级。有终身着力。亦不能至者。是故虽其言致知言克己言力行言理言心言仁义。而其归宿则只在于识得此心当下便是。而既能识得此心当下便是。则无安排无计较。胸中流出。无非自然。从心行得。尽是天理。此心此理。便是天地之心。便是圣人之心。而其徒所谓因扇讼是非。忽省此心之清明。无始末无不通。而以日月之明。四时之变化。天地之广大。鬼神之不可测。赞其师之心。仍言其与万古之人心。一贯无二致。其师生传授言论若此。而气象急迫。言语过高。工夫太易。阶级大躐。主张太过。无进修之积。无穷格之烦。未尝费一日下学之工。而直欲以一朝意识之测度。超百年实践之境界。正是朱夫子所谓江西顿悟。教人禅会。而勉斋所谓守虚灵之识。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文佛老之说者。惟此二言而其学术之误。流弊之巨。可推而知矣。况其既见得后方做工夫。则朱子已斥之以上达下学。与圣贤之训不同。其议论之常觉两头明中间暗。则朱子又以禅家自爱之说。捉现其真赃。而惟此中间之所以暗。自爱之外又有一段公案。盖此心之妙。无形迹无方所。难以言语形
若其足目俱到。实为己有。则自有无限工程。无穷阶级。有终身着力。亦不能至者。是故虽其言致知言克己言力行言理言心言仁义。而其归宿则只在于识得此心当下便是。而既能识得此心当下便是。则无安排无计较。胸中流出。无非自然。从心行得。尽是天理。此心此理。便是天地之心。便是圣人之心。而其徒所谓因扇讼是非。忽省此心之清明。无始末无不通。而以日月之明。四时之变化。天地之广大。鬼神之不可测。赞其师之心。仍言其与万古之人心。一贯无二致。其师生传授言论若此。而气象急迫。言语过高。工夫太易。阶级大躐。主张太过。无进修之积。无穷格之烦。未尝费一日下学之工。而直欲以一朝意识之测度。超百年实践之境界。正是朱夫子所谓江西顿悟。教人禅会。而勉斋所谓守虚灵之识。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文佛老之说者。惟此二言而其学术之误。流弊之巨。可推而知矣。况其既见得后方做工夫。则朱子已斥之以上达下学。与圣贤之训不同。其议论之常觉两头明中间暗。则朱子又以禅家自爱之说。捉现其真赃。而惟此中间之所以暗。自爱之外又有一段公案。盖此心之妙。无形迹无方所。难以言语形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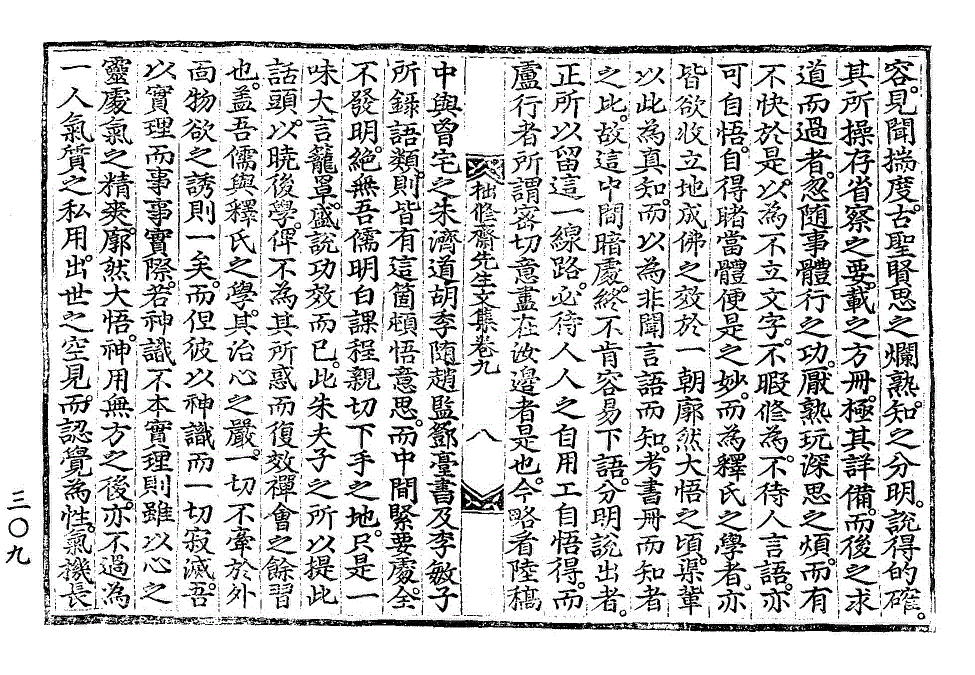 容。见闻揣度。古圣贤思之烂熟。知之分明。说得的确。其所操存省察之要。载之方册。极其详备。而后之求道而过者。忽随事体行之功。厌熟玩深思之烦。而有不快于是。以为不立文字。不暇修为。不待人言语。亦可自悟。自得睹当体便是之妙。而为释氏之学者。亦皆欲收立地成佛之效于一朝廓然大悟之顷。渠辈以此为真知。而以为非闻言语而知。考书册而知者之比。故这中间暗处。终不肯容易下语。分明说出者。正所以留这一线路。必待人人之自用工自悟得。而卢行者所谓密切意尽在汝边者是也。今略看陆稿中与曾宅之朱济道,胡季随,赵监,邓台书及李敏子所录语类。则皆有这个顿悟意思。而中间紧要处。全不发明。绝无吾儒明白课程亲切下手之地。只是一味大言笼罩。盛说功效而已。此朱夫子之所以提此话头。以晓后学。俾不为其所惑而复效禅会之馀习也。盖吾儒与释氏之学。其治心之严。一切不牵于外面物欲之诱则一矣。而但彼以神识而一切寂灭。吾以实理而事事实际。若神识不本实理则虽以心之灵处气之精爽。廓然大悟。神用无方之后。亦不过为一人气质之私用。出世之空见。而认觉为性。气机长
容。见闻揣度。古圣贤思之烂熟。知之分明。说得的确。其所操存省察之要。载之方册。极其详备。而后之求道而过者。忽随事体行之功。厌熟玩深思之烦。而有不快于是。以为不立文字。不暇修为。不待人言语。亦可自悟。自得睹当体便是之妙。而为释氏之学者。亦皆欲收立地成佛之效于一朝廓然大悟之顷。渠辈以此为真知。而以为非闻言语而知。考书册而知者之比。故这中间暗处。终不肯容易下语。分明说出者。正所以留这一线路。必待人人之自用工自悟得。而卢行者所谓密切意尽在汝边者是也。今略看陆稿中与曾宅之朱济道,胡季随,赵监,邓台书及李敏子所录语类。则皆有这个顿悟意思。而中间紧要处。全不发明。绝无吾儒明白课程亲切下手之地。只是一味大言笼罩。盛说功效而已。此朱夫子之所以提此话头。以晓后学。俾不为其所惑而复效禅会之馀习也。盖吾儒与释氏之学。其治心之严。一切不牵于外面物欲之诱则一矣。而但彼以神识而一切寂灭。吾以实理而事事实际。若神识不本实理则虽以心之灵处气之精爽。廓然大悟。神用无方之后。亦不过为一人气质之私用。出世之空见。而认觉为性。气机长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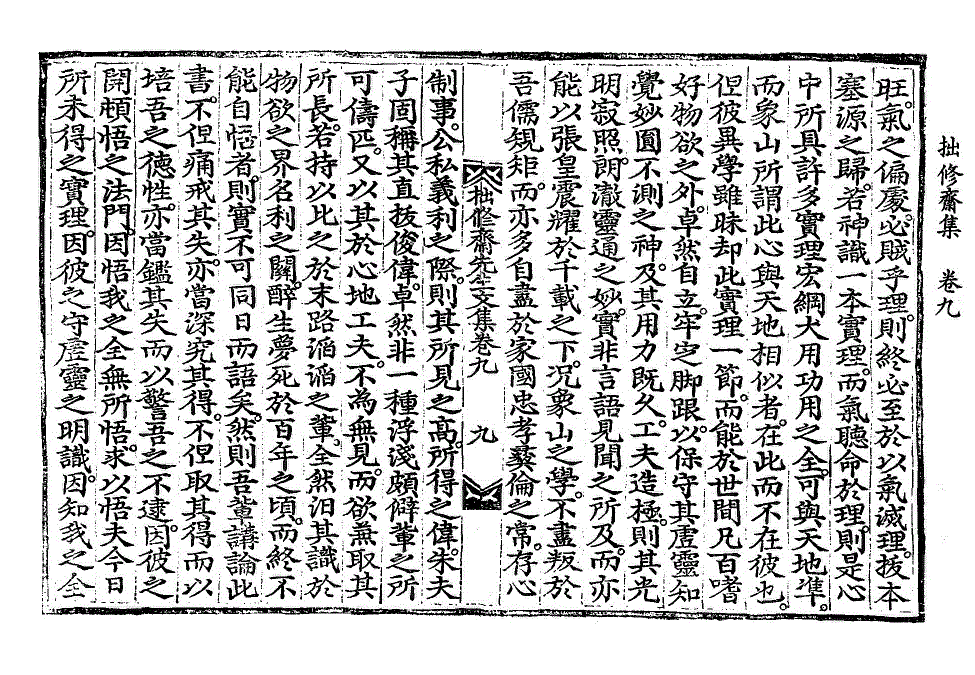 旺。气之偏处。必贼乎理。则终必至于以气灭理。拔本塞源之归。若神识一本实理。而气听命于理。则是心中所具许多实理宏纲大用功用之全。可与天地准。而象山所谓此心与天地相似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但彼异学虽昧却此实理一节。而能于世间凡百嗜好物欲之外。卓然自立。牢定脚跟。以保守其虚灵知觉妙圆不测之神。及其用力既久。工夫造极。则其光明寂照。朗澈灵通之妙。实非言语见闻之所及。而亦能以张皇震耀于千载之下。况象山之学。不尽叛于吾儒规矩。而亦多自尽于家国忠孝彝伦之常。存心制事。公私义利之际。则其所见之高。所得之伟。朱夫子固称其直拔俊伟。卓然非一种浮浅颇僻辈之所可俦匹。又以其于心地工夫。不为无见。而欲兼取其所长。若持以比之于末路滔滔之辈。全然汩其识于物欲之界名利之关。醉生梦死于百年之顷。而终不能自悟者。则实不可同日而语矣。然则吾辈讲论此书。不但痛戒其失。亦当深究其得。不但取其得而以培吾之德性。亦当鉴其失而以警吾之不逮。因彼之开顿悟之法门。因悟我之全无所悟。求以悟夫今日所未得之实理。因彼之守虚灵之明识。因知我之全
旺。气之偏处。必贼乎理。则终必至于以气灭理。拔本塞源之归。若神识一本实理。而气听命于理。则是心中所具许多实理宏纲大用功用之全。可与天地准。而象山所谓此心与天地相似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但彼异学虽昧却此实理一节。而能于世间凡百嗜好物欲之外。卓然自立。牢定脚跟。以保守其虚灵知觉妙圆不测之神。及其用力既久。工夫造极。则其光明寂照。朗澈灵通之妙。实非言语见闻之所及。而亦能以张皇震耀于千载之下。况象山之学。不尽叛于吾儒规矩。而亦多自尽于家国忠孝彝伦之常。存心制事。公私义利之际。则其所见之高。所得之伟。朱夫子固称其直拔俊伟。卓然非一种浮浅颇僻辈之所可俦匹。又以其于心地工夫。不为无见。而欲兼取其所长。若持以比之于末路滔滔之辈。全然汩其识于物欲之界名利之关。醉生梦死于百年之顷。而终不能自悟者。则实不可同日而语矣。然则吾辈讲论此书。不但痛戒其失。亦当深究其得。不但取其得而以培吾之德性。亦当鉴其失而以警吾之不逮。因彼之开顿悟之法门。因悟我之全无所悟。求以悟夫今日所未得之实理。因彼之守虚灵之明识。因知我之全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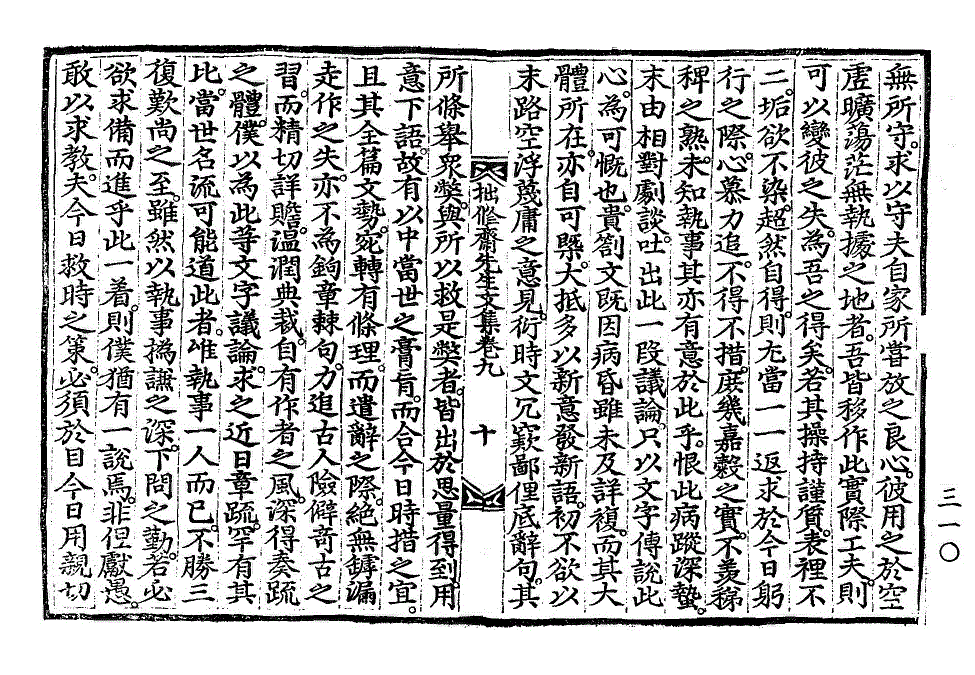 无所守。求以守夫自家所尝放之良心。彼用之于空虚旷荡茫无执据之地者。吾皆移作此实际工夫。则可以变彼之失。为吾之得矣。若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垢欲不染。超然自得。则尤当一一返求于今日躬行之际。心慕力追。不得不措。庶几嘉谷之实。不羡稊稗之熟。未知执事其亦有意于此乎。恨此病踪深蛰。末由相对剧谈。吐出此一段议论。只以文字传说此心。为可慨也。贵劄文既因病昏虽未及详复。而其大体所在。亦自可槩。大抵多以新意发新语。初不欲以末路空浮蔑庸之意见。衍时文冗窾鄙俚底辞句。其所条举众弊。与所以救是弊者。皆出于思量得到。用意下语。故有以中当世之膏肓。而合今日时措之宜。且其全篇文势。宛转有条理。而遣辞之际。绝无罅漏走作之失。亦不为钩章棘句。力追古人险僻奇古之习。而精切详赡。温润典裁。自有作者之风。深得奏疏之体。仆以为此等文字议论。求之近日章疏。罕有其比。当世名流可能道此者。唯执事一人而已。不胜三复叹尚之至。虽然以执事撝谦之深。下问之勤。若必欲求备而进乎此一着。则仆犹有一说焉。非但献愚。敢以求教。夫今日救时之策。必须于目今日用亲切
无所守。求以守夫自家所尝放之良心。彼用之于空虚旷荡茫无执据之地者。吾皆移作此实际工夫。则可以变彼之失。为吾之得矣。若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垢欲不染。超然自得。则尤当一一返求于今日躬行之际。心慕力追。不得不措。庶几嘉谷之实。不羡稊稗之熟。未知执事其亦有意于此乎。恨此病踪深蛰。末由相对剧谈。吐出此一段议论。只以文字传说此心。为可慨也。贵劄文既因病昏虽未及详复。而其大体所在。亦自可槩。大抵多以新意发新语。初不欲以末路空浮蔑庸之意见。衍时文冗窾鄙俚底辞句。其所条举众弊。与所以救是弊者。皆出于思量得到。用意下语。故有以中当世之膏肓。而合今日时措之宜。且其全篇文势。宛转有条理。而遣辞之际。绝无罅漏走作之失。亦不为钩章棘句。力追古人险僻奇古之习。而精切详赡。温润典裁。自有作者之风。深得奏疏之体。仆以为此等文字议论。求之近日章疏。罕有其比。当世名流可能道此者。唯执事一人而已。不胜三复叹尚之至。虽然以执事撝谦之深。下问之勤。若必欲求备而进乎此一着。则仆犹有一说焉。非但献愚。敢以求教。夫今日救时之策。必须于目今日用亲切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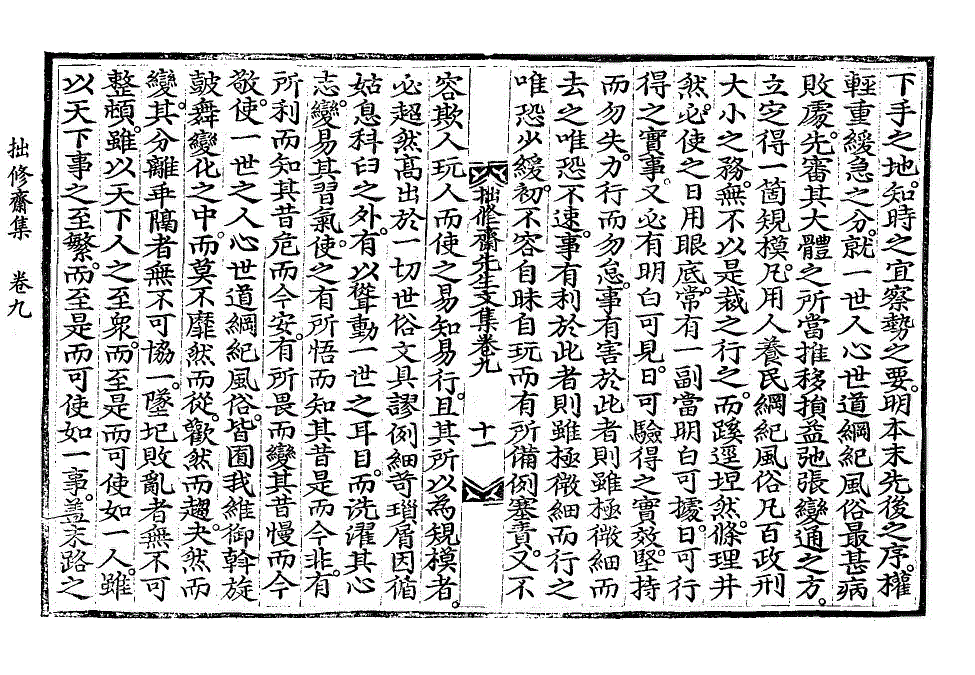 下手之地。知时之宜察势之要。明本末先后之序。权轻重缓急之分。就一世人心世道纲纪风俗最甚病败处。先审其大体之所当推移损益弛张变通之方。立定得一个规模。凡用人养民纲纪风俗凡百政刑大小之务。无不以是裁之行之。而蹊径坦然。条理井然。必使之日用眼底。常有一副当明白可据。日可行得之实事。又必有明白可见。日可验得之实效。坚持而勿失。力行而勿怠。事有害于此者则虽极微细而去之唯恐不速。事有利于此者则虽极微细而行之唯恐少缓。初不容自昧自玩而有所备例塞责。又不容欺人玩人而使之易知易行。且其所以为规模者。必超然高出于一切世俗文具谬例细苟琐屑因循姑息科臼之外。有以耸动一世之耳目。而洗濯其心志。变易其习气。使之有所悟而知其昔是而今非。有所利而知其昔危而今安。有所畏而变其昔慢而今敬。使一世之人心世道纲纪风俗。皆囿我维御斡旋鼓舞变化之中。而莫不靡然而从。欢然而趋。夬然而变。其分离乖隔者无不可协一。坠圮败乱者无不可整顿。虽以天下人之至众。而至是而可使如一人。虽以天下事之至繁。而至是而可使如一事。盖末路之
下手之地。知时之宜察势之要。明本末先后之序。权轻重缓急之分。就一世人心世道纲纪风俗最甚病败处。先审其大体之所当推移损益弛张变通之方。立定得一个规模。凡用人养民纲纪风俗凡百政刑大小之务。无不以是裁之行之。而蹊径坦然。条理井然。必使之日用眼底。常有一副当明白可据。日可行得之实事。又必有明白可见。日可验得之实效。坚持而勿失。力行而勿怠。事有害于此者则虽极微细而去之唯恐不速。事有利于此者则虽极微细而行之唯恐少缓。初不容自昧自玩而有所备例塞责。又不容欺人玩人而使之易知易行。且其所以为规模者。必超然高出于一切世俗文具谬例细苟琐屑因循姑息科臼之外。有以耸动一世之耳目。而洗濯其心志。变易其习气。使之有所悟而知其昔是而今非。有所利而知其昔危而今安。有所畏而变其昔慢而今敬。使一世之人心世道纲纪风俗。皆囿我维御斡旋鼓舞变化之中。而莫不靡然而从。欢然而趋。夬然而变。其分离乖隔者无不可协一。坠圮败乱者无不可整顿。虽以天下人之至众。而至是而可使如一人。虽以天下事之至繁。而至是而可使如一事。盖末路之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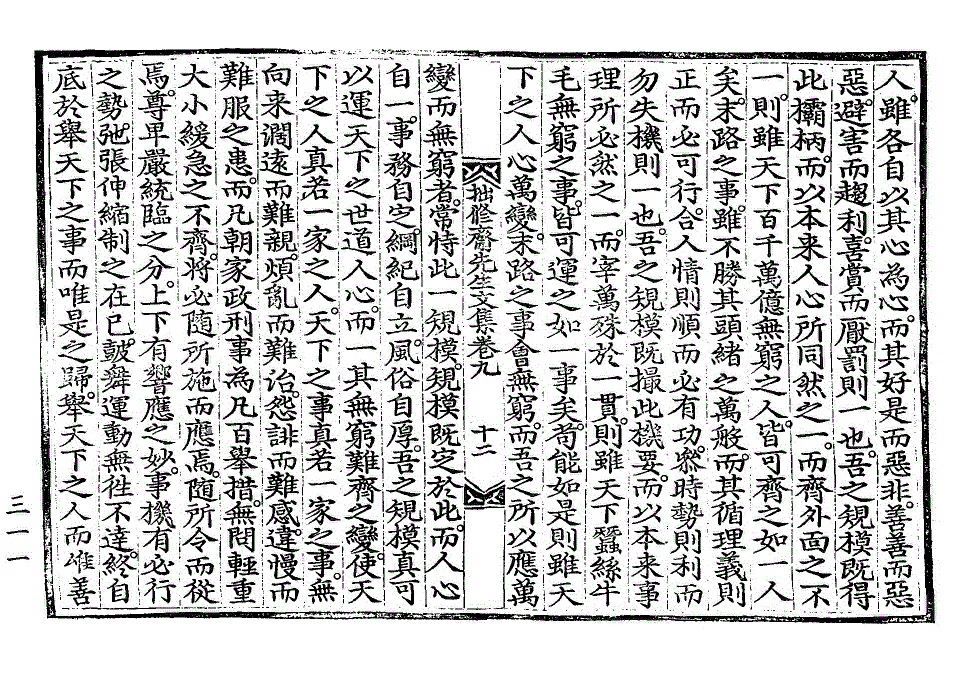 人。虽各自以其心为心。而其好是而恶非。善善而恶恶。避害而趋利。喜赏而厌罚则一也。吾之规模既得此把柄。而以本来人心所同然之一。而齐外面之不一。则虽天下百千万亿无穷之人。皆可齐之如一人矣。末路之事。虽不胜其头绪之万般。而其循理义则正而必可行。合人情则顺而必有功。参时势则利而勿失机则一也。吾之规模既撮此机要。而以本来事理所必然之一。而宰万殊于一贯。则虽天下蚕丝牛毛无穷之事。皆可运之如一事矣。苟能如是则虽天下之人心万变。末路之事会无穷。而吾之所以应万变而无穷者。常恃此一规模。规模既定于此。而人心自一。事务自定。纲纪自立。风俗自厚。吾之规模真可以运天下之世道人心。而一其无穷难齐之变。使天下之人真若一家之人。天下之事真若一家之事。无向来阔远而难亲。烦乱而难治。怨诽而难感。违慢而难服之患。而凡朝家政刑事为凡百举措。无问轻重大小缓急之不齐。将必随所施而应焉。随所令而从焉。尊卑严统临之分。上下有响应之妙。事机有必行之势。弛张伸缩制之在已。鼓舞运动无往不达。终自底于举天下之事而唯是之归。举天下之人而唯善
人。虽各自以其心为心。而其好是而恶非。善善而恶恶。避害而趋利。喜赏而厌罚则一也。吾之规模既得此把柄。而以本来人心所同然之一。而齐外面之不一。则虽天下百千万亿无穷之人。皆可齐之如一人矣。末路之事。虽不胜其头绪之万般。而其循理义则正而必可行。合人情则顺而必有功。参时势则利而勿失机则一也。吾之规模既撮此机要。而以本来事理所必然之一。而宰万殊于一贯。则虽天下蚕丝牛毛无穷之事。皆可运之如一事矣。苟能如是则虽天下之人心万变。末路之事会无穷。而吾之所以应万变而无穷者。常恃此一规模。规模既定于此。而人心自一。事务自定。纲纪自立。风俗自厚。吾之规模真可以运天下之世道人心。而一其无穷难齐之变。使天下之人真若一家之人。天下之事真若一家之事。无向来阔远而难亲。烦乱而难治。怨诽而难感。违慢而难服之患。而凡朝家政刑事为凡百举措。无问轻重大小缓急之不齐。将必随所施而应焉。随所令而从焉。尊卑严统临之分。上下有响应之妙。事机有必行之势。弛张伸缩制之在已。鼓舞运动无往不达。终自底于举天下之事而唯是之归。举天下之人而唯善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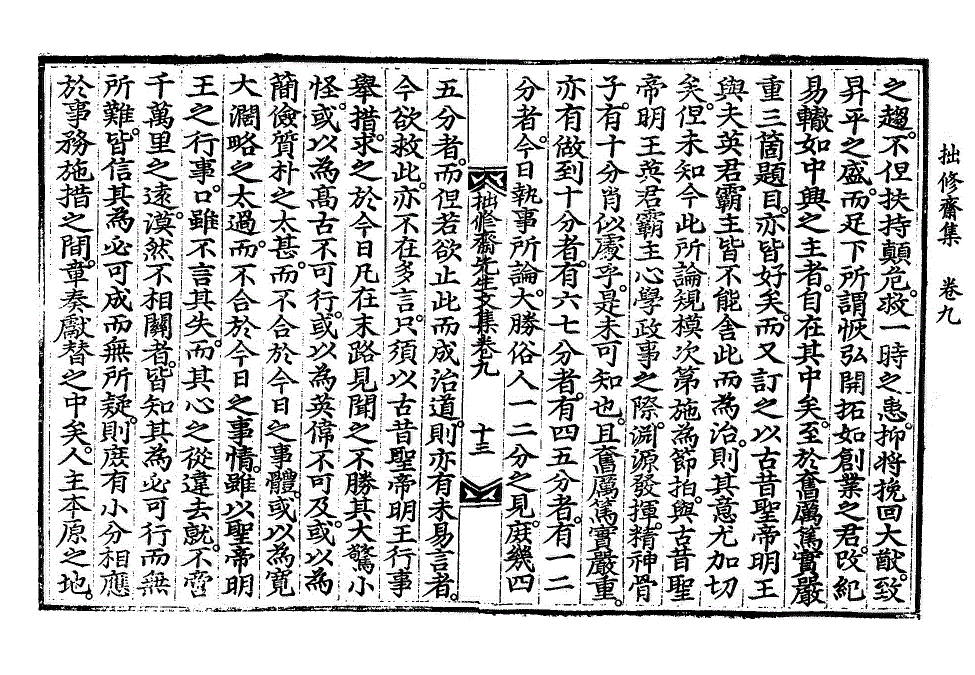 之趋。不但扶持颠危。救一时之患。抑将挽回大猷。致升平之盛。而足下所谓恢弘开拓如创业之君。改纪易辙如中兴之主者。自在其中矣。至于奋厉笃实严重三个题目。亦皆好矣。而又订之以古昔圣帝明王与夫英君霸主皆不能舍此而为治。则其意尤加切矣。但未知今此所论规模次第施为节拍。与古昔圣帝明王英君霸主心学政事之际。渊源发挥。精神骨子。有十分肖似处乎。是未可知也。且奋厉笃实严重。亦有做到十分者。有六七分者。有四五分者。有一二分者。今日执事所论。大胜俗人一二分之见。庶几四五分者。而但若欲止此而成治道。则亦有未易言者。今欲救此。亦不在多言。只须以古昔圣帝明王行事举措。求之于今日凡在末路见闻之不胜其大惊小怪。或以为高古不可行。或以为英伟不可及。或以为简俭质朴之太甚。而不合于今日之事体。或以为宽大阔略之太过。而不合于今日之事情。虽以圣帝明王之行事。口虽不言其失。而其心之从违去就。不啻千万里之远。漠然不相关者。皆知其为必可行而无所难。皆信其为必可成而无所疑。则庶有小分相应于事务施措之间。章奏献替之中矣。人主本原之地。
之趋。不但扶持颠危。救一时之患。抑将挽回大猷。致升平之盛。而足下所谓恢弘开拓如创业之君。改纪易辙如中兴之主者。自在其中矣。至于奋厉笃实严重三个题目。亦皆好矣。而又订之以古昔圣帝明王与夫英君霸主皆不能舍此而为治。则其意尤加切矣。但未知今此所论规模次第施为节拍。与古昔圣帝明王英君霸主心学政事之际。渊源发挥。精神骨子。有十分肖似处乎。是未可知也。且奋厉笃实严重。亦有做到十分者。有六七分者。有四五分者。有一二分者。今日执事所论。大胜俗人一二分之见。庶几四五分者。而但若欲止此而成治道。则亦有未易言者。今欲救此。亦不在多言。只须以古昔圣帝明王行事举措。求之于今日凡在末路见闻之不胜其大惊小怪。或以为高古不可行。或以为英伟不可及。或以为简俭质朴之太甚。而不合于今日之事体。或以为宽大阔略之太过。而不合于今日之事情。虽以圣帝明王之行事。口虽不言其失。而其心之从违去就。不啻千万里之远。漠然不相关者。皆知其为必可行而无所难。皆信其为必可成而无所疑。则庶有小分相应于事务施措之间。章奏献替之中矣。人主本原之地。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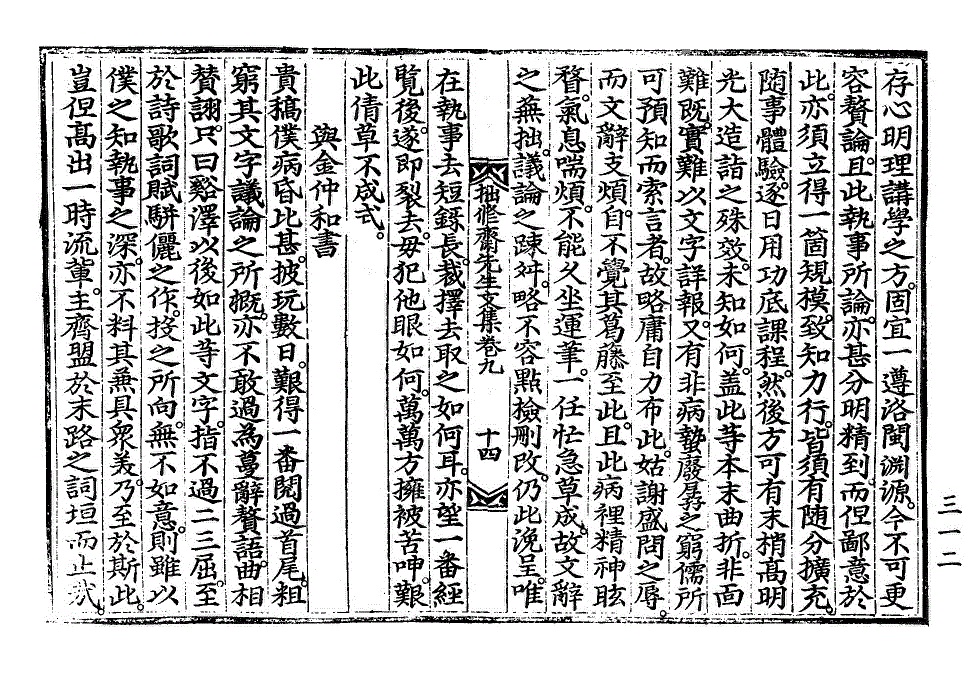 存心明理讲学之方。固宜一遵洛闽渊源。今不可更容赘论。且此执事所论。亦甚分明精到。而但鄙意于此。亦须立得一个规模。致知力行。皆须有随分扩充。随事体验。逐日用功底课程。然后方可有末梢高明光大造诣之殊效。未知如何。盖此等本末曲折。非面难既。实难以文字详报。又有非病蛰废孱之穷儒所可预知而索言者。故略庸自力布此。姑谢盛问之辱。而文辞支烦。自不觉其葛藤至此。且此病里精神眩瞀。气息喘烦。不能久坐运笔。一任忙急草成。故文辞之芜拙。议论之疏舛。略不容点检删改。仍此浼呈。唯在执事去短录长。裁择去取之如何耳。亦望一番经览后。遂即裂去。毋犯他眼如何。万万方拥被苦呻。艰此倩草不成式。
存心明理讲学之方。固宜一遵洛闽渊源。今不可更容赘论。且此执事所论。亦甚分明精到。而但鄙意于此。亦须立得一个规模。致知力行。皆须有随分扩充。随事体验。逐日用功底课程。然后方可有末梢高明光大造诣之殊效。未知如何。盖此等本末曲折。非面难既。实难以文字详报。又有非病蛰废孱之穷儒所可预知而索言者。故略庸自力布此。姑谢盛问之辱。而文辞支烦。自不觉其葛藤至此。且此病里精神眩瞀。气息喘烦。不能久坐运笔。一任忙急草成。故文辞之芜拙。议论之疏舛。略不容点检删改。仍此浼呈。唯在执事去短录长。裁择去取之如何耳。亦望一番经览后。遂即裂去。毋犯他眼如何。万万方拥被苦呻。艰此倩草不成式。与金仲和书
贵稿仆病昏比甚。披玩数日。艰得一番阅过首尾。粗穷其文字议论之所概。亦不敢过为蔓辞赘语。曲相赞诩。只曰溪泽以后如此等文字。指不过二三屈。至于诗歌词赋骈俪之作。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则虽以仆之知执事之深。亦不料其兼具众美。乃至于斯此。岂但高出一时流辈。主齐盟于末路之词垣而止哉。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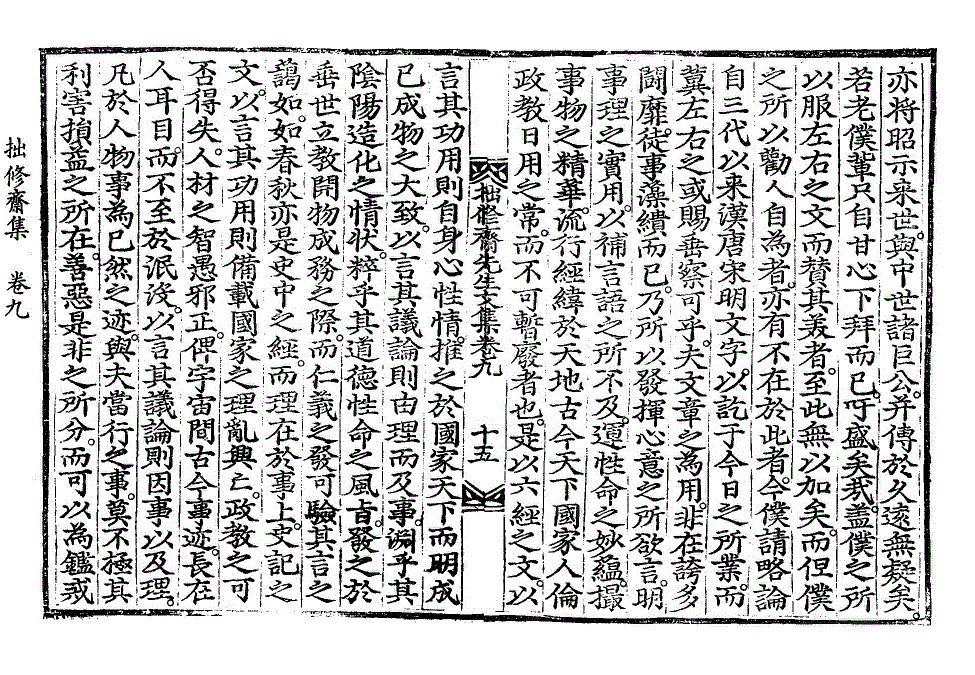 亦将昭示来世。与中世诸巨公。并传于久远无疑矣。若老仆辈只自甘心下拜而已。吁盛矣哉。盖仆之所以服左右之文而赞其美者。至此无以加矣。而但仆之所以劝人自为者。亦有不在于此者。今仆请略论自三代以来汉唐宋明文字。以讫于今日之所业。而冀左右之或赐垂察可乎。夫文章之为用。非在誇多斗靡。徒事藻缋而已。乃所以发挥心意之所欲言。明事理之实用。以补言语之所不及。运性命之妙蕴。撮事物之精华。流行经纬于天地古今天下国家人伦政教日用之常。而不可暂废者也。是以六经之文。以言其功用则自身心性情。推之于国家天下而明成己成物之大致。以言其议论则由理而及事。渊乎其阴阳造化之情状。粹乎其道德性命之风旨。发之于垂世立教开物成务之际。而仁义之发可验其言之蔼如。如春秋亦是史中之经。而理在于事上。史记之文。以言其功用则备载国家之理乱兴亡。政教之可否得失。人材之智愚邪正。俾宇宙间古今事迹。长在人耳目。而不至于泯没。以言其议论则因事以及理。凡于人物事为已然之迹。与夫当行之事。莫不极其利害损益之所在。善恶是非之所分。而可以为鉴戒
亦将昭示来世。与中世诸巨公。并传于久远无疑矣。若老仆辈只自甘心下拜而已。吁盛矣哉。盖仆之所以服左右之文而赞其美者。至此无以加矣。而但仆之所以劝人自为者。亦有不在于此者。今仆请略论自三代以来汉唐宋明文字。以讫于今日之所业。而冀左右之或赐垂察可乎。夫文章之为用。非在誇多斗靡。徒事藻缋而已。乃所以发挥心意之所欲言。明事理之实用。以补言语之所不及。运性命之妙蕴。撮事物之精华。流行经纬于天地古今天下国家人伦政教日用之常。而不可暂废者也。是以六经之文。以言其功用则自身心性情。推之于国家天下而明成己成物之大致。以言其议论则由理而及事。渊乎其阴阳造化之情状。粹乎其道德性命之风旨。发之于垂世立教开物成务之际。而仁义之发可验其言之蔼如。如春秋亦是史中之经。而理在于事上。史记之文。以言其功用则备载国家之理乱兴亡。政教之可否得失。人材之智愚邪正。俾宇宙间古今事迹。长在人耳目。而不至于泯没。以言其议论则因事以及理。凡于人物事为已然之迹。与夫当行之事。莫不极其利害损益之所在。善恶是非之所分。而可以为鉴戒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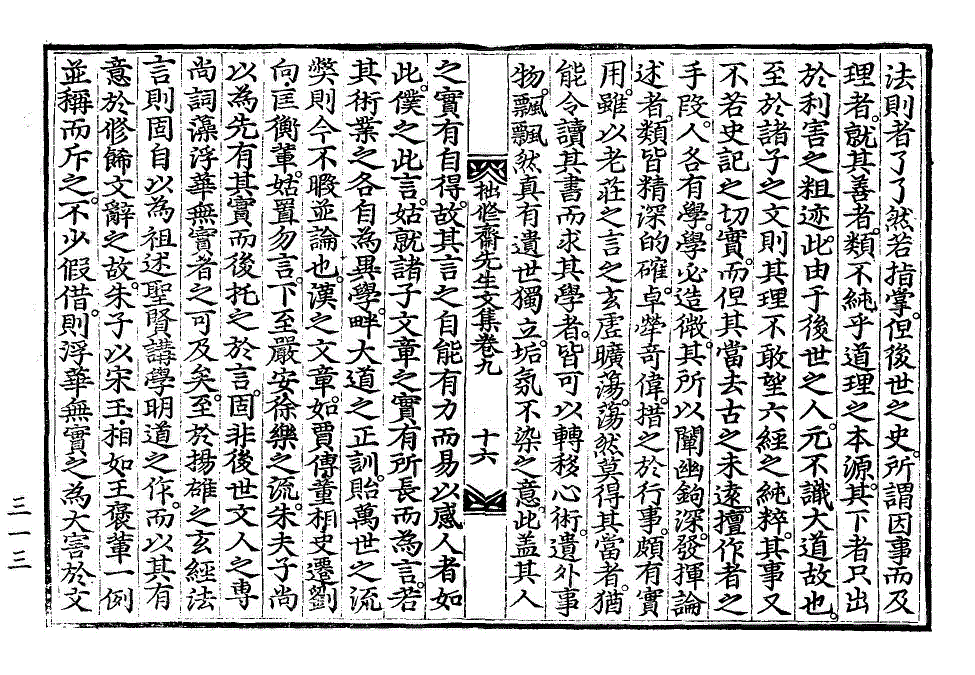 法则者了了然若指掌。但后世之史。所谓因事而及理者。就其善者。类不纯乎道理之本源。其下者只出于利害之粗迹。此由于后世之人。元不识大道故也。至于诸子之文则其理不敢望六经之纯粹。其事又不若史记之切实。而但其当去古之未远。擅作者之手段。人各有学。学必造微。其所以阐幽钩深。发挥论述者。类皆精深的确。卓荦奇伟。措之于行事。颇有实用。虽以老庄之言之玄虚旷荡。荡然莫得其当者。犹能令读其书而求其学者。皆可以转移心术。遗外事物。飘飘然真有遗世独立。垢氛不染之意。此盖其人之实有自得。故其言之自能有力而易以感人者如此。仆之此言。姑就诸子文章之实有所长而为言。若其术业之各自为异学。畔大道之正训。贻万世之流弊则今不暇并论也。汉之文章。如贾传,董相,史迁,刘向,匡衡辈。姑置勿言。下至严安,徐乐之流。朱夫子尚以为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固非后世文人之专尚词藻浮华无实者之可及矣。至于扬雄之玄经法言则固自以为祖述圣贤讲学明道之作。而以其有意于修饰文辞之故。朱子以宋玉,相如,王褒辈一例并称而斥之。不少假借。则浮华无实之为大害于文
法则者了了然若指掌。但后世之史。所谓因事而及理者。就其善者。类不纯乎道理之本源。其下者只出于利害之粗迹。此由于后世之人。元不识大道故也。至于诸子之文则其理不敢望六经之纯粹。其事又不若史记之切实。而但其当去古之未远。擅作者之手段。人各有学。学必造微。其所以阐幽钩深。发挥论述者。类皆精深的确。卓荦奇伟。措之于行事。颇有实用。虽以老庄之言之玄虚旷荡。荡然莫得其当者。犹能令读其书而求其学者。皆可以转移心术。遗外事物。飘飘然真有遗世独立。垢氛不染之意。此盖其人之实有自得。故其言之自能有力而易以感人者如此。仆之此言。姑就诸子文章之实有所长而为言。若其术业之各自为异学。畔大道之正训。贻万世之流弊则今不暇并论也。汉之文章。如贾传,董相,史迁,刘向,匡衡辈。姑置勿言。下至严安,徐乐之流。朱夫子尚以为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固非后世文人之专尚词藻浮华无实者之可及矣。至于扬雄之玄经法言则固自以为祖述圣贤讲学明道之作。而以其有意于修饰文辞之故。朱子以宋玉,相如,王褒辈一例并称而斥之。不少假借。则浮华无实之为大害于文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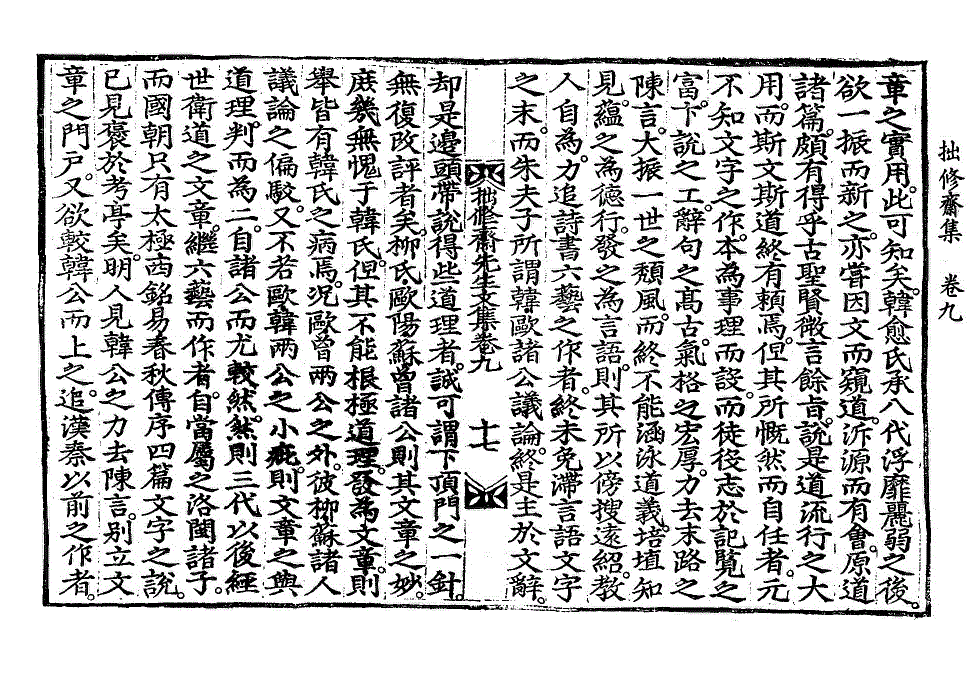 章之实用。此可知矣。韩愈氏承八代浮靡丽弱之后。欲一振而新之。亦尝因文而窥道。溯源而有会。原道诸篇。颇有得乎古圣贤微言馀旨。说是道流行之大用。而斯文斯道终有赖焉。但其所慨然而自任者。元不知文字之作。本为事理而设。而徒役志于记览之富。卞说之工。辞句之高古。气格之宏厚。力去末路之陈言。大振一世之颓风。而终不能涵泳道义。培埴知见。蕴之为德行。发之为言语。则其所以傍搜远绍。教人自为。力追诗书六艺之作者。终未免滞言语文字之末。而朱夫子所谓韩,欧诸公议论。终是主于文辞。却是边头带说得些道理者。诚可谓下顶门之一针。无复改评者矣。柳氏,欧阳,苏,曾诸公则其文章之妙。庶几无愧于韩氏。但其不能根极道理。发为文章。则举皆有韩氏之病焉。况欧,曾两公之外。彼柳,苏诸人议论之偏驳。又不若欧,韩两公之小疵。则文章之与道理。判而为二。自诸公而尤较然。然则三代以后经世卫道之文章。继六艺而作者。自当属之洛闽诸子。而国朝只有太极,西铭,易,春秋传序四篇文字之说。己见褒于考亭矣。明人见韩公之力去陈言。别立文章之门户。又欲较韩公而上之。追汉秦以前之作者。
章之实用。此可知矣。韩愈氏承八代浮靡丽弱之后。欲一振而新之。亦尝因文而窥道。溯源而有会。原道诸篇。颇有得乎古圣贤微言馀旨。说是道流行之大用。而斯文斯道终有赖焉。但其所慨然而自任者。元不知文字之作。本为事理而设。而徒役志于记览之富。卞说之工。辞句之高古。气格之宏厚。力去末路之陈言。大振一世之颓风。而终不能涵泳道义。培埴知见。蕴之为德行。发之为言语。则其所以傍搜远绍。教人自为。力追诗书六艺之作者。终未免滞言语文字之末。而朱夫子所谓韩,欧诸公议论。终是主于文辞。却是边头带说得些道理者。诚可谓下顶门之一针。无复改评者矣。柳氏,欧阳,苏,曾诸公则其文章之妙。庶几无愧于韩氏。但其不能根极道理。发为文章。则举皆有韩氏之病焉。况欧,曾两公之外。彼柳,苏诸人议论之偏驳。又不若欧,韩两公之小疵。则文章之与道理。判而为二。自诸公而尤较然。然则三代以后经世卫道之文章。继六艺而作者。自当属之洛闽诸子。而国朝只有太极,西铭,易,春秋传序四篇文字之说。己见褒于考亭矣。明人见韩公之力去陈言。别立文章之门户。又欲较韩公而上之。追汉秦以前之作者。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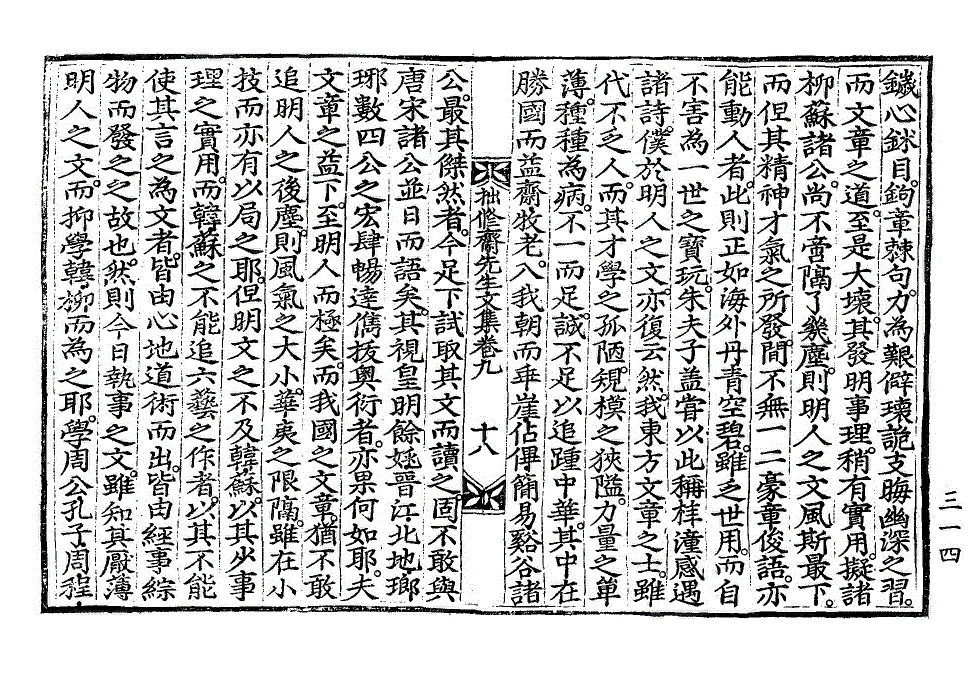 鐬心鉥目。钩章棘句。力为艰僻环诡支晦幽深之习。而文章之道。至是大坏。其发明事理。稍有实用。拟诸柳苏诸公。尚不啻隔了几尘。则明人之文风斯最下。而但其精神才气之所发。间不无一二豪章俊语。亦能动人者。此则正如海外丹青空碧。虽乏世用。而自不害为一世之宝玩。朱夫子盖尝以此称桂潼感遇诸诗。仆于明人之文。亦复云然。我东方文章之士。虽代不乏人。而其才学之孤陋。规模之狭隘。力量之单薄。种种为病。不一而足。诚不足以追踵中华。其中在胜国而益斋,牧老。入我朝而乖崖,佔毕,简易,溪谷诸公。最其杰然者。今足下试取其文而读之。固不敢与唐宋诸公并日而语矣。其视皇明馀姚,晋江,北地,琅琊数四公之宏肆畅达俊拔奥衍者。亦果何如耶。夫文章之益下。至明人而极矣。而我国之文章。犹不敢追明人之后尘。则风气之大小。华夷之限隔。虽在小技而亦有以局之耶。但明文之不及韩,苏。以其少事理之实用。而韩,苏之不能追六艺之作者。以其不能使其言之为文者。皆由心地道术而出。皆由经事综物而发之之故也。然则今日执事之文。虽知其厌薄明人之文。而抑学韩,柳而为之耶。学周公,孔子,周,程,
鐬心鉥目。钩章棘句。力为艰僻环诡支晦幽深之习。而文章之道。至是大坏。其发明事理。稍有实用。拟诸柳苏诸公。尚不啻隔了几尘。则明人之文风斯最下。而但其精神才气之所发。间不无一二豪章俊语。亦能动人者。此则正如海外丹青空碧。虽乏世用。而自不害为一世之宝玩。朱夫子盖尝以此称桂潼感遇诸诗。仆于明人之文。亦复云然。我东方文章之士。虽代不乏人。而其才学之孤陋。规模之狭隘。力量之单薄。种种为病。不一而足。诚不足以追踵中华。其中在胜国而益斋,牧老。入我朝而乖崖,佔毕,简易,溪谷诸公。最其杰然者。今足下试取其文而读之。固不敢与唐宋诸公并日而语矣。其视皇明馀姚,晋江,北地,琅琊数四公之宏肆畅达俊拔奥衍者。亦果何如耶。夫文章之益下。至明人而极矣。而我国之文章。犹不敢追明人之后尘。则风气之大小。华夷之限隔。虽在小技而亦有以局之耶。但明文之不及韩,苏。以其少事理之实用。而韩,苏之不能追六艺之作者。以其不能使其言之为文者。皆由心地道术而出。皆由经事综物而发之之故也。然则今日执事之文。虽知其厌薄明人之文。而抑学韩,柳而为之耶。学周公,孔子,周,程,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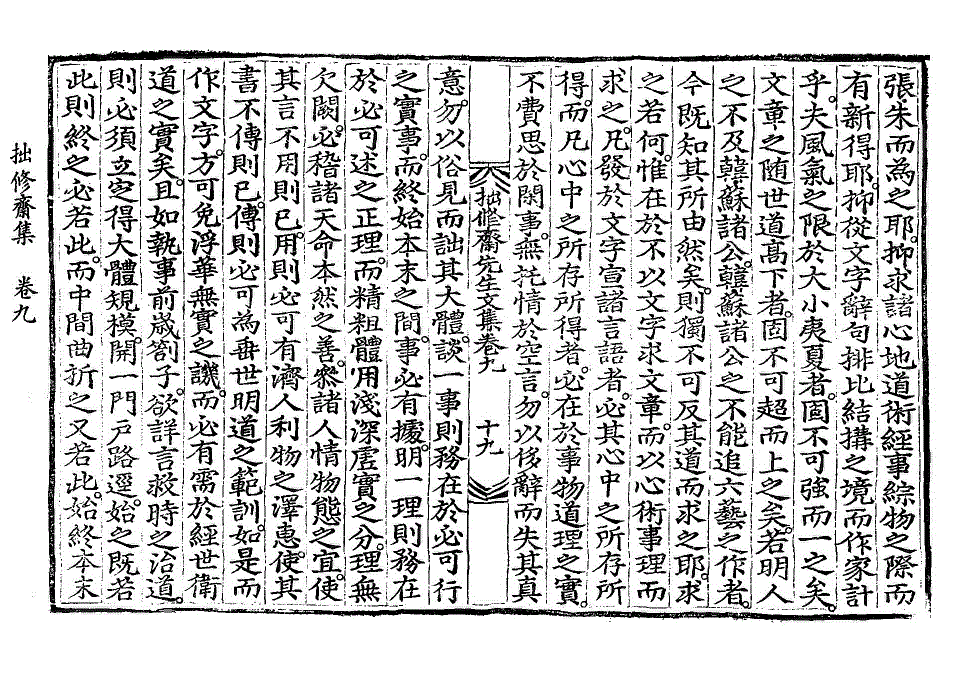 张,朱而为之耶。抑求诸心地道术经事综物之际而有新得耶。抑从文字辞句排比结搆之境而作家计乎。夫风气之限于大小夷夏者。固不可强而一之矣。文章之随世道高下者。固不可超而上之矣。若明人之不及韩,苏诸公。韩,苏诸公之不能追六艺之作者。今既知其所由然矣。则独不可反其道而求之耶。求之若何。惟在于不以文字求文章。而以心术事理而求之。凡发于文字宣诸言语者。必其心中之所存所得。而凡心中之所存所得者。必在于事物道理之实。不费思于闲事。无托情于空言。勿以侈辞而失其真意。勿以俗见而诎其大体。谈一事则务在于必可行之实事。而终始本末之间。事必有据。明一理则务在于必可述之正理。而精粗体用浅深虚实之分。理无欠阙。必稽诸天命本然之善。参诸人情物态之宜。使其言不用则已。用则必可有济人利物之泽惠。使其书不传则已。传则必可为垂世明道之范训。如是而作文字。方可免浮华无实之讥。而必有需于经世卫道之实矣。且如执事前岁劄子。欲详言救时之治道。则必须立定得大体规模。开一门户路径。始之既若此则终之必若此。而中间曲折之又若此。始终本末
张,朱而为之耶。抑求诸心地道术经事综物之际而有新得耶。抑从文字辞句排比结搆之境而作家计乎。夫风气之限于大小夷夏者。固不可强而一之矣。文章之随世道高下者。固不可超而上之矣。若明人之不及韩,苏诸公。韩,苏诸公之不能追六艺之作者。今既知其所由然矣。则独不可反其道而求之耶。求之若何。惟在于不以文字求文章。而以心术事理而求之。凡发于文字宣诸言语者。必其心中之所存所得。而凡心中之所存所得者。必在于事物道理之实。不费思于闲事。无托情于空言。勿以侈辞而失其真意。勿以俗见而诎其大体。谈一事则务在于必可行之实事。而终始本末之间。事必有据。明一理则务在于必可述之正理。而精粗体用浅深虚实之分。理无欠阙。必稽诸天命本然之善。参诸人情物态之宜。使其言不用则已。用则必可有济人利物之泽惠。使其书不传则已。传则必可为垂世明道之范训。如是而作文字。方可免浮华无实之讥。而必有需于经世卫道之实矣。且如执事前岁劄子。欲详言救时之治道。则必须立定得大体规模。开一门户路径。始之既若此则终之必若此。而中间曲折之又若此。始终本末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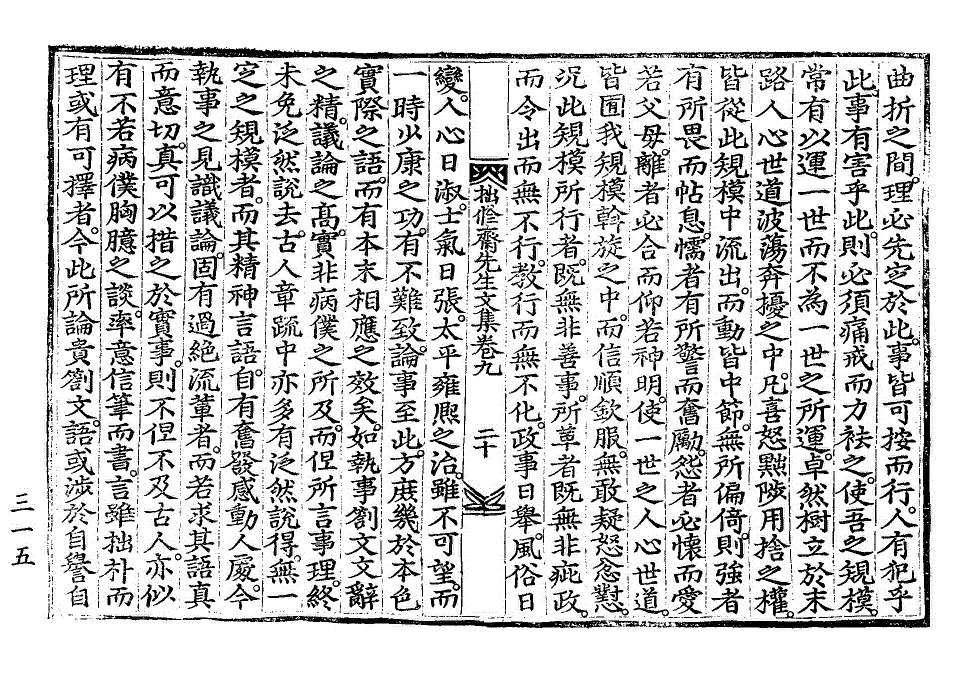 曲折之间。理必先定于此。事皆可按而行。人有犯乎此。事有害乎此。则必须痛戒而力袪之。使吾之规模。常有以运一世而不为一世之所运。卓然树立于末路人心世道波荡奔扰之中。凡喜怒黜陟用舍之权。皆从此规模中流出。而动皆中节。无所偏倚。则强者有所畏而帖息。懦者有所警而奋励。怨者必怀而爱若父母。离者必合而仰若神明。使一世之人心世道。皆囿我规模斡旋之中。而信顺钦服。无敢疑怒忿怼。况此规模所行者。既无非善事。所革者既无非疵政。而令出而无不行。教行而无不化。政事日举。风俗日变。人心日淑。士气日张。太平雍熙之治。虽不可望。而一时少康之功。有不难致。论事至此。方庶几于本色实际之语。而有本末相应之效矣。如执事劄文文辞之精。议论之高。实非病仆之所及。而但所言事理。终未免泛然说去。古人章疏中亦多有泛然说得。无一定之规模者。而其精神言语。自有奋发感动人处。今执事之见识议论。固有过绝流辈者。而若求其语真而意切。真可以措之于实事。则不但不及古人。亦似有不若病仆胸臆之谈。率意信笔而书。言虽拙朴而理或有可择者。今此所论贵劄文。语或涉于自誉自
曲折之间。理必先定于此。事皆可按而行。人有犯乎此。事有害乎此。则必须痛戒而力袪之。使吾之规模。常有以运一世而不为一世之所运。卓然树立于末路人心世道波荡奔扰之中。凡喜怒黜陟用舍之权。皆从此规模中流出。而动皆中节。无所偏倚。则强者有所畏而帖息。懦者有所警而奋励。怨者必怀而爱若父母。离者必合而仰若神明。使一世之人心世道。皆囿我规模斡旋之中。而信顺钦服。无敢疑怒忿怼。况此规模所行者。既无非善事。所革者既无非疵政。而令出而无不行。教行而无不化。政事日举。风俗日变。人心日淑。士气日张。太平雍熙之治。虽不可望。而一时少康之功。有不难致。论事至此。方庶几于本色实际之语。而有本末相应之效矣。如执事劄文文辞之精。议论之高。实非病仆之所及。而但所言事理。终未免泛然说去。古人章疏中亦多有泛然说得。无一定之规模者。而其精神言语。自有奋发感动人处。今执事之见识议论。固有过绝流辈者。而若求其语真而意切。真可以措之于实事。则不但不及古人。亦似有不若病仆胸臆之谈。率意信笔而书。言虽拙朴而理或有可择者。今此所论贵劄文。语或涉于自誉自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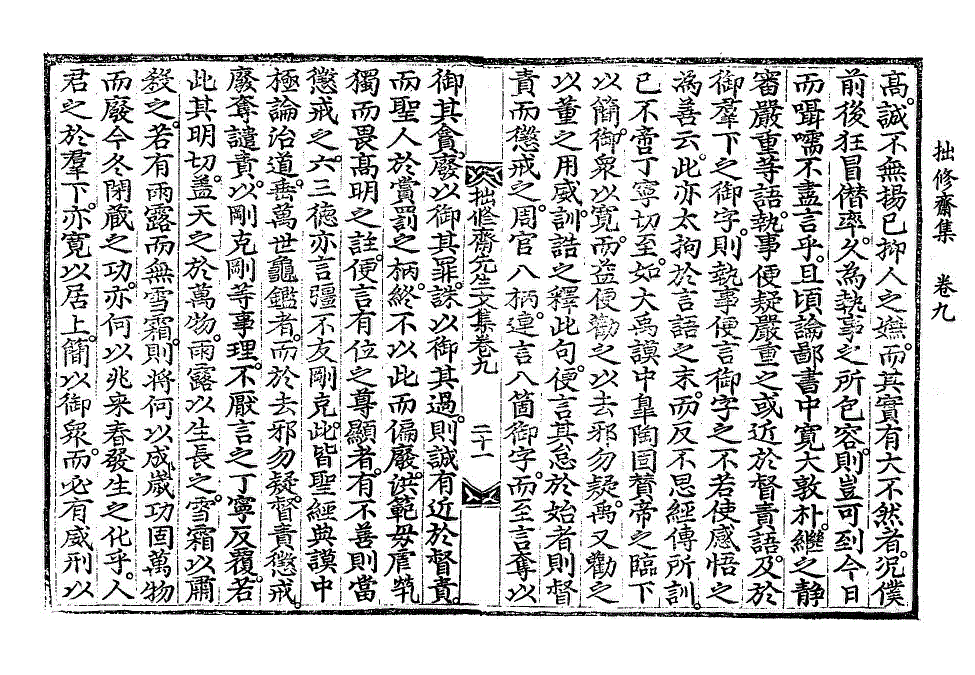 高。诚不无扬己抑人之嫌。而其实有大不然者。况仆前后狂冒僭率。久为执事之所包容。则岂可到今日而嗫嚅不尽言乎。且顷论鄙书中宽大敦朴。继之静审严重等语。执事便疑严重之或近于督责语。及于御群下之御字。则执事便言御字之不若使感悟之为善云。此亦太拘于言语之末。而反不思经传所训。已不啻丁宁切至。如大禹谟中皋陶固赞帝之临下以简。御众以宽。而益便劝之以去邪勿疑。禹又劝之以董之用威。训诰之释此句。便言其怠于始者则督责而惩戒之。周官八柄。连言八个御字。而至言夺以御其贪。废以御其罪。诛以御其过。则诚有近于督责。而圣人于赏罚之柄。终不以此而偏废。洪范毋虐茕独而畏高明之注。便言有位之尊显者。有不善则当惩戒之。六三德亦言彊不友刚克。此皆圣经典谟中极论治道。垂万世龟鉴者。而于去邪勿疑。督责惩戒。废夺谴责。以刚克刚等事理。不厌言之丁宁反覆。若此其明切。盖天之于万物。雨露以生长之。雪霜以肃杀之。若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将何以成岁功固万物而废今冬闭藏之功。亦何以兆来春发生之化乎。人君之于群下。亦宽以居上。简以御众。而必有威刑以
高。诚不无扬己抑人之嫌。而其实有大不然者。况仆前后狂冒僭率。久为执事之所包容。则岂可到今日而嗫嚅不尽言乎。且顷论鄙书中宽大敦朴。继之静审严重等语。执事便疑严重之或近于督责语。及于御群下之御字。则执事便言御字之不若使感悟之为善云。此亦太拘于言语之末。而反不思经传所训。已不啻丁宁切至。如大禹谟中皋陶固赞帝之临下以简。御众以宽。而益便劝之以去邪勿疑。禹又劝之以董之用威。训诰之释此句。便言其怠于始者则督责而惩戒之。周官八柄。连言八个御字。而至言夺以御其贪。废以御其罪。诛以御其过。则诚有近于督责。而圣人于赏罚之柄。终不以此而偏废。洪范毋虐茕独而畏高明之注。便言有位之尊显者。有不善则当惩戒之。六三德亦言彊不友刚克。此皆圣经典谟中极论治道。垂万世龟鉴者。而于去邪勿疑。督责惩戒。废夺谴责。以刚克刚等事理。不厌言之丁宁反覆。若此其明切。盖天之于万物。雨露以生长之。雪霜以肃杀之。若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将何以成岁功固万物而废今冬闭藏之功。亦何以兆来春发生之化乎。人君之于群下。亦宽以居上。简以御众。而必有威刑以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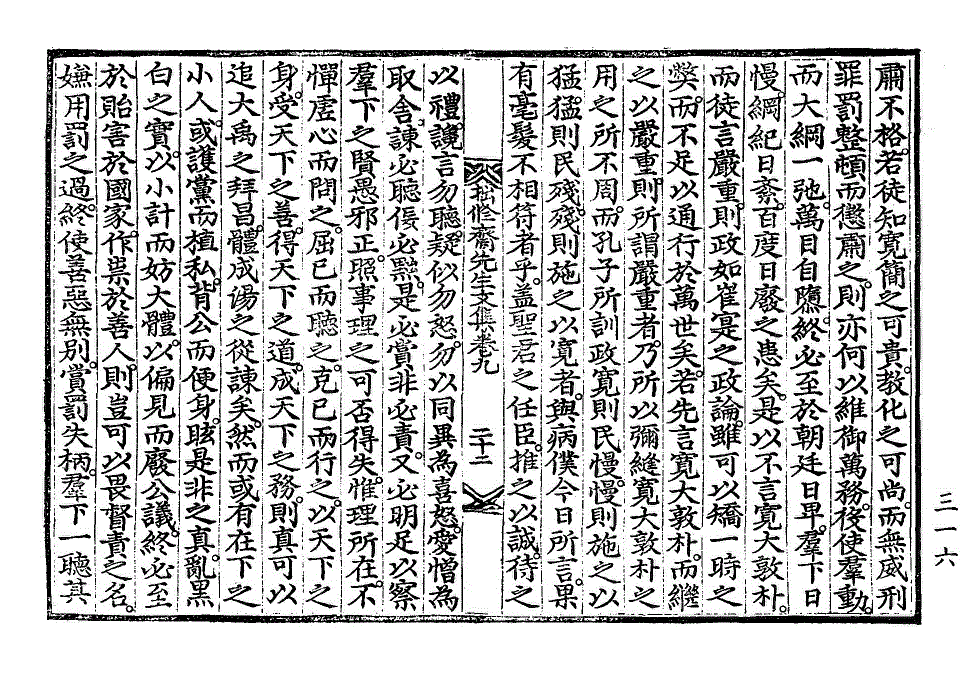 肃不格。若徒知宽简之可贵。教化之可尚。而无威刑罪罚整顿而惩肃之。则亦何以维御万务。役使群动。而大纲一弛。万目自隳。终必至于朝廷日卑。群下日慢。纲纪日紊。百度日废之患矣。是以不言宽大敦朴。而徒言严重。则政如崔寔之政论。虽可以矫一时之弊。而不足以通行于万世矣。若先言宽大敦朴。而继之以严重。则所谓严重者。乃所以弥缝宽大敦朴之用之所不周。而孔子所训政宽则民慢。慢则施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者。与病仆今日所言。果有毫发不相符者乎。盖圣君之任臣。推之以诚。待之以礼。谗言勿听。疑似勿怒。勿以同异为喜怒。爱憎为取舍。谏必听佞必黜。是必赏非必责。又必明足以察群下之贤愚邪正。照事理之可否得失。惟理所在。不惮虚心而问之。屈己而听之。克己而行之。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则真可以追大禹之拜昌。体成汤之从谏矣。然而或有在下之小人。或护党而植私。背公而便身。眩是非之真。乱黑白之实。以小计而妨大体。以偏见而废公议。终必至于贻害于国家。作祟于善人。则岂可以畏督责之名。嫌用罚之过。终使善恶无别。赏罚失柄。群下一听其
肃不格。若徒知宽简之可贵。教化之可尚。而无威刑罪罚整顿而惩肃之。则亦何以维御万务。役使群动。而大纲一弛。万目自隳。终必至于朝廷日卑。群下日慢。纲纪日紊。百度日废之患矣。是以不言宽大敦朴。而徒言严重。则政如崔寔之政论。虽可以矫一时之弊。而不足以通行于万世矣。若先言宽大敦朴。而继之以严重。则所谓严重者。乃所以弥缝宽大敦朴之用之所不周。而孔子所训政宽则民慢。慢则施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者。与病仆今日所言。果有毫发不相符者乎。盖圣君之任臣。推之以诚。待之以礼。谗言勿听。疑似勿怒。勿以同异为喜怒。爱憎为取舍。谏必听佞必黜。是必赏非必责。又必明足以察群下之贤愚邪正。照事理之可否得失。惟理所在。不惮虚心而问之。屈己而听之。克己而行之。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则真可以追大禹之拜昌。体成汤之从谏矣。然而或有在下之小人。或护党而植私。背公而便身。眩是非之真。乱黑白之实。以小计而妨大体。以偏见而废公议。终必至于贻害于国家。作祟于善人。则岂可以畏督责之名。嫌用罚之过。终使善恶无别。赏罚失柄。群下一听其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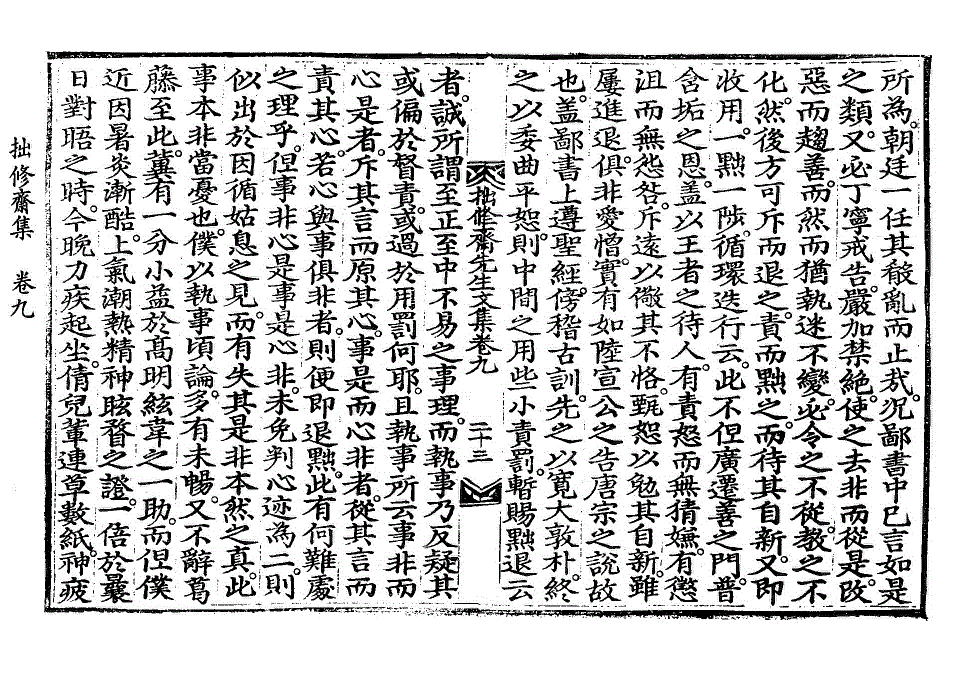 所为。朝廷一任其殽乱而止哉。况鄙书中已言如是之类。又必丁宁戒告。严加禁绝。使之去非而从是。改恶而趋善。而然而犹执迷不变。必令之不从。教之不化。然后方可斥而退之。责而黜之。而待其自新。又即收用。一黜一陟。循环迭行云。此不但广迁善之门。普含垢之恩。盖以王者之待人。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咎。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虽屡进退。俱非爱憎。实有如陆宣公之告唐宗之说故也。盖鄙书上遵圣经。傍稽古训。先之以宽大敦朴。终之以委曲平恕。则中间之用些小责罚。暂赐黜退云者。诚所谓至正至中不易之事理。而执事乃反疑其或偏于督责。或过于用罚何耶。且执事所云事非而心是者。斥其言而原其心。事是而心非者。从其言而责其心。若心与事俱非者。则便即退黜。此有何难处之理乎。但事非心是事是心非。未免判心迹为二。则似出于因循姑息之见。而有失其是非本然之真。此事本非当忧也。仆以执事顷论。多有未畅。又不辞葛藤至此。冀有一分小益于高明弦韦之一助。而但仆近因暑炎渐酷。上气潮热精神眩瞀之證。一倍于曩日对晤之时。今晚力疾起坐。倩儿辈连草数纸。神疲
所为。朝廷一任其殽乱而止哉。况鄙书中已言如是之类。又必丁宁戒告。严加禁绝。使之去非而从是。改恶而趋善。而然而犹执迷不变。必令之不从。教之不化。然后方可斥而退之。责而黜之。而待其自新。又即收用。一黜一陟。循环迭行云。此不但广迁善之门。普含垢之恩。盖以王者之待人。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咎。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虽屡进退。俱非爱憎。实有如陆宣公之告唐宗之说故也。盖鄙书上遵圣经。傍稽古训。先之以宽大敦朴。终之以委曲平恕。则中间之用些小责罚。暂赐黜退云者。诚所谓至正至中不易之事理。而执事乃反疑其或偏于督责。或过于用罚何耶。且执事所云事非而心是者。斥其言而原其心。事是而心非者。从其言而责其心。若心与事俱非者。则便即退黜。此有何难处之理乎。但事非心是事是心非。未免判心迹为二。则似出于因循姑息之见。而有失其是非本然之真。此事本非当忧也。仆以执事顷论。多有未畅。又不辞葛藤至此。冀有一分小益于高明弦韦之一助。而但仆近因暑炎渐酷。上气潮热精神眩瞀之證。一倍于曩日对晤之时。今晚力疾起坐。倩儿辈连草数纸。神疲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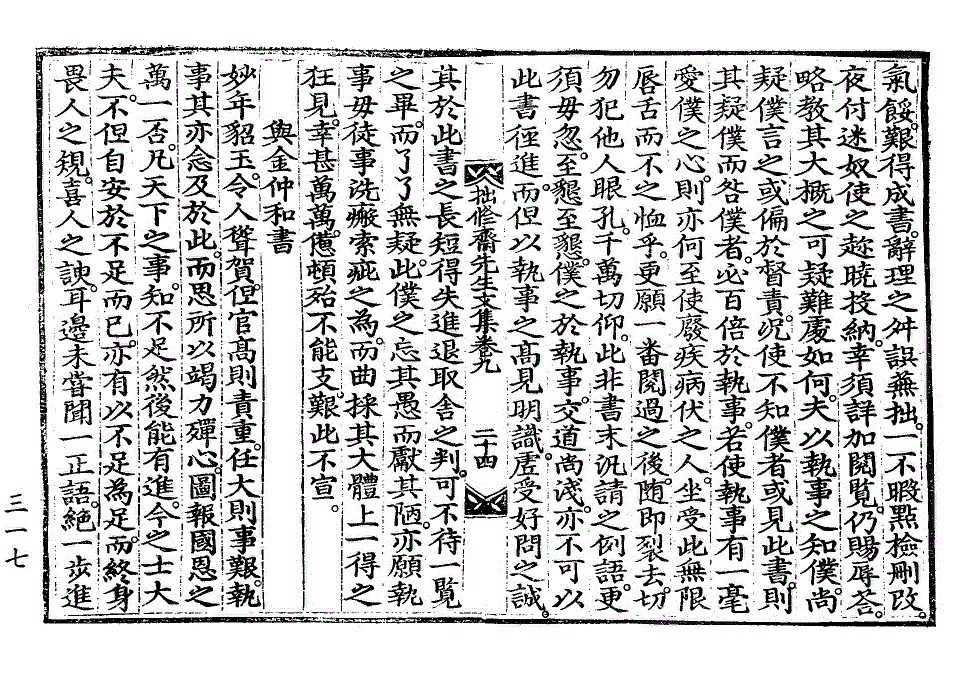 气馁。艰得成书。辞理之舛误芜拙。一不暇点检删改。夜付迷奴使之趁晓投纳。幸须详加阅览。仍赐辱答。略教其大概之可疑难处如何。夫以执事之知仆。尚疑仆言之或偏于督责。况使不知仆者或见此书。则其疑仆而咎仆者。必百倍于执事。若使执事有一毫爱仆之心。则亦何至使废疾病伏之人。坐受此无限唇舌而不之恤乎。更愿一番阅过之后。随即裂去。切勿犯他人眼孔。千万切仰。此非书末汎请之例语。更须毋忽。至恳至恳。仆之于执事。交道尚浅。亦不可以此书径进。而但以执事之高见明识。虚受好问之诚。其于此书之长短得失进退取舍之判。可不待一览之毕。而了了无疑。此仆之忘其愚而献其陋。亦愿执事毋徒事洗瘢索疵之为。而曲采其大体上一得之狂见。幸甚万万。惫顿殆不能支。艰此不宣。
气馁。艰得成书。辞理之舛误芜拙。一不暇点检删改。夜付迷奴使之趁晓投纳。幸须详加阅览。仍赐辱答。略教其大概之可疑难处如何。夫以执事之知仆。尚疑仆言之或偏于督责。况使不知仆者或见此书。则其疑仆而咎仆者。必百倍于执事。若使执事有一毫爱仆之心。则亦何至使废疾病伏之人。坐受此无限唇舌而不之恤乎。更愿一番阅过之后。随即裂去。切勿犯他人眼孔。千万切仰。此非书末汎请之例语。更须毋忽。至恳至恳。仆之于执事。交道尚浅。亦不可以此书径进。而但以执事之高见明识。虚受好问之诚。其于此书之长短得失进退取舍之判。可不待一览之毕。而了了无疑。此仆之忘其愚而献其陋。亦愿执事毋徒事洗瘢索疵之为。而曲采其大体上一得之狂见。幸甚万万。惫顿殆不能支。艰此不宣。与金仲和书
妙年貂玉。令人耸贺。但官高则责重。任大则事艰。执事其亦念及于此。而思所以竭力殚心。图报国恩之万一否。凡天下之事。知不足然后能有进。今之士大夫。不但自安于不足而已。亦有以不足为足。而终身畏人之规。喜人之谀。耳边未尝闻一正语。绝一步进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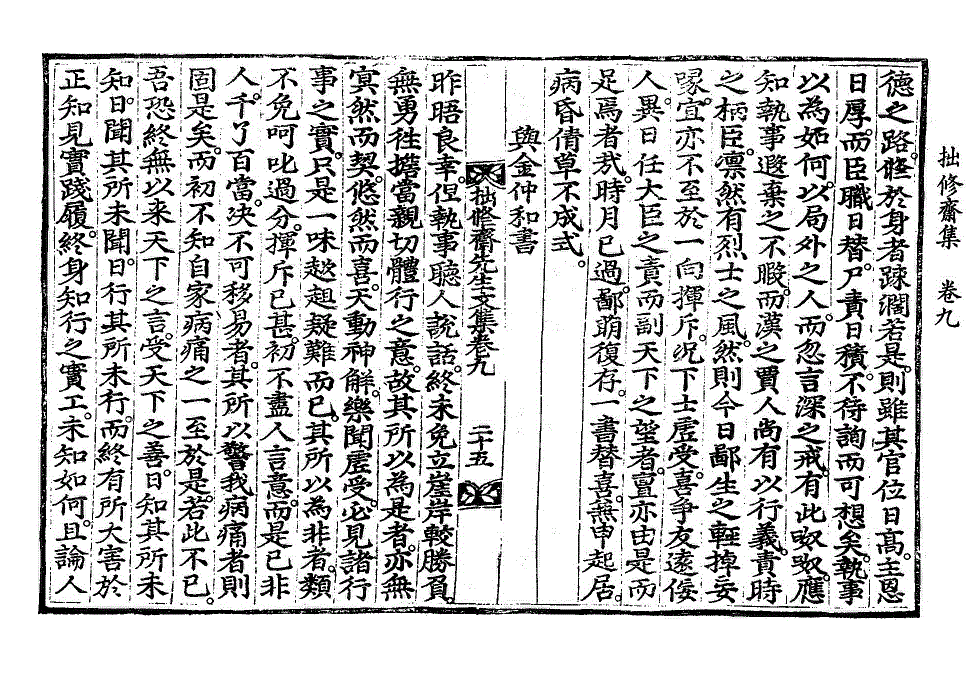 德之路。修于身者疏阔若是。则虽其官位日高。主恩日厚。而臣职日替。尸责日积。不待询而可想矣。执事以为如何。以局外之人。而忽言深之戒。有此呶呶。应知执事遐弃之不暇。而汉之贾人尚有以行义。责时之柄臣。凛然有烈士之风。然则今日鄙生之轻掉妄喙。宜亦不至于一向挥斥。况下士虚受。喜争友远佞人。异日任大臣之责而副天下之望者。亶亦由是而足焉者哉。时月已过。鄙萌复存。一书替喜。兼申起居。病昏倩草不成式。
德之路。修于身者疏阔若是。则虽其官位日高。主恩日厚。而臣职日替。尸责日积。不待询而可想矣。执事以为如何。以局外之人。而忽言深之戒。有此呶呶。应知执事遐弃之不暇。而汉之贾人尚有以行义。责时之柄臣。凛然有烈士之风。然则今日鄙生之轻掉妄喙。宜亦不至于一向挥斥。况下士虚受。喜争友远佞人。异日任大臣之责而副天下之望者。亶亦由是而足焉者哉。时月已过。鄙萌复存。一书替喜。兼申起居。病昏倩草不成式。与金仲和书
昨晤良幸。但执事听人说话。终未免立崖岸较胜负。无勇往担当亲切体行之意。故其所以为是者。亦无冥然而契。悠然而喜。天动神解。乐闻虚受。必见诸行事之实。只是一味趑趄疑难而已。其所以为非者。类不免呵叱过分。挥斥已甚。初不尽人言意。而是己非人。千了百当。决不可移易者。其所以警我病痛者则固是矣。而初不知自家病痛之一至于是。若此不已。吾恐终无以来天下之言。受天下之善。日知其所未知。日闻其所未闻。日行其所未行。而终有所大害于正知见实践履。终身知行之实工。未知如何。且论人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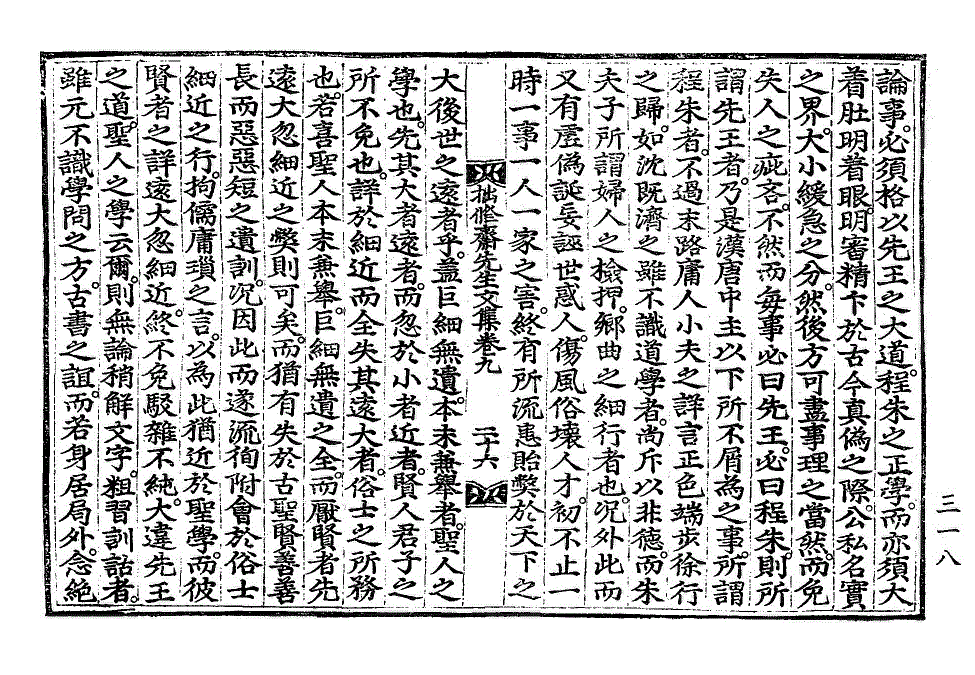 论事。必须格以先王之大道。程朱之正学。而亦须大着肚明着眼。明审精卞于古今真伪之际。公私名实之界。大小缓急之分。然后方可尽事理之当然。而免失人之疵吝。不然而每事必曰先王。必曰程朱。则所谓先王者。乃是汉唐中主以下所不屑为之事。所谓程朱者。不过末路庸人小夫之详言正色端步徐行之归。如沈既济之虽不识道学者。尚斥以非德。而朱夫子所谓妇人之检押。乡曲之细行者也。况外此而又有虚伪诞妄诬世惑人。伤风俗坏人才。初不止一时一事一人一家之害。终有所流患贻弊于天下之大后世之远者乎。盖巨细无遗。本末兼举者。圣人之学也。先其大者远者。而忽于小者近者。贤人君子之所不免也。详于细近而全失其远大者。俗士之所务也。若喜圣人本末兼举。巨细无遗之全。而厌贤者先远大忽细近之弊则可矣。而犹有失于古圣贤善善长而恶恶短之遗训。况因此而遂流徇附会于俗士细近之行。拘儒庸琐之言。以为此犹近于圣学。而彼贤者之详远大忽细近。终不免驳杂不纯。大违先王之道。圣人之学云尔。则无论稍解文字。粗习训诂者。虽元不识学问之方。古书之谊。而若身居局外。念绝
论事。必须格以先王之大道。程朱之正学。而亦须大着肚明着眼。明审精卞于古今真伪之际。公私名实之界。大小缓急之分。然后方可尽事理之当然。而免失人之疵吝。不然而每事必曰先王。必曰程朱。则所谓先王者。乃是汉唐中主以下所不屑为之事。所谓程朱者。不过末路庸人小夫之详言正色端步徐行之归。如沈既济之虽不识道学者。尚斥以非德。而朱夫子所谓妇人之检押。乡曲之细行者也。况外此而又有虚伪诞妄诬世惑人。伤风俗坏人才。初不止一时一事一人一家之害。终有所流患贻弊于天下之大后世之远者乎。盖巨细无遗。本末兼举者。圣人之学也。先其大者远者。而忽于小者近者。贤人君子之所不免也。详于细近而全失其远大者。俗士之所务也。若喜圣人本末兼举。巨细无遗之全。而厌贤者先远大忽细近之弊则可矣。而犹有失于古圣贤善善长而恶恶短之遗训。况因此而遂流徇附会于俗士细近之行。拘儒庸琐之言。以为此犹近于圣学。而彼贤者之详远大忽细近。终不免驳杂不纯。大违先王之道。圣人之学云尔。则无论稍解文字。粗习训诂者。虽元不识学问之方。古书之谊。而若身居局外。念绝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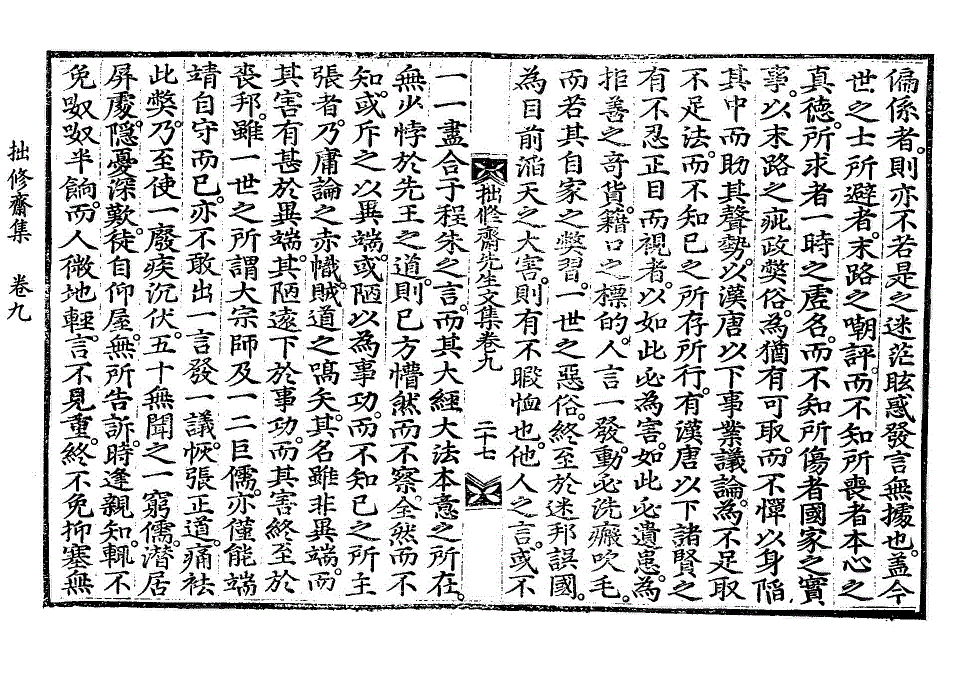 偏系者。则亦不若是之迷茫眩惑发言无据也。盖今世之士所避者。末路之嘲评。而不知所丧者本心之真德。所求者一时之虚名。而不知所伤者国家之实事。以末路之疵政弊俗。为犹有可取。而不惮以身陷其中而助其声势。以汉唐以下事业议论。为不足取不足法。而不知己之所存所行。有汉唐以下诸贤之有不忍正目而视者。以如此必为害。如此必遗患。为拒善之奇货。籍口之标的。人言一发。动必洗瘢吹毛。而若其自家之弊习。一世之恶俗。终至于迷邦误国。为目前滔天之大害。则有不暇恤也。他人之言。或不一一尽合于程朱之言。而其大经大法本意之所在。无少悖于先王之道。则己方懵然而不察。全然而不知。或斥之以异端。或陋以为事功。而不知己之所主张者。乃庸论之赤帜。贼道之嗃矢。其名虽非异端。而其害有甚于异端。其陋远下于事功。而其害终至于丧邦。虽一世之所谓大宗师及一二巨儒。亦仅能端靖自守而已。亦不敢出一言发一议。恢张正道。痛袪此弊。乃至使一废疾沈伏。五十无闻之一穷儒。潜居屏处。隐忧深叹。徒自仰屋。无所告诉。时逢亲知。辄不免呶呶半饷。而人微地轻。言不见重。终不免抑塞无
偏系者。则亦不若是之迷茫眩惑发言无据也。盖今世之士所避者。末路之嘲评。而不知所丧者本心之真德。所求者一时之虚名。而不知所伤者国家之实事。以末路之疵政弊俗。为犹有可取。而不惮以身陷其中而助其声势。以汉唐以下事业议论。为不足取不足法。而不知己之所存所行。有汉唐以下诸贤之有不忍正目而视者。以如此必为害。如此必遗患。为拒善之奇货。籍口之标的。人言一发。动必洗瘢吹毛。而若其自家之弊习。一世之恶俗。终至于迷邦误国。为目前滔天之大害。则有不暇恤也。他人之言。或不一一尽合于程朱之言。而其大经大法本意之所在。无少悖于先王之道。则己方懵然而不察。全然而不知。或斥之以异端。或陋以为事功。而不知己之所主张者。乃庸论之赤帜。贼道之嗃矢。其名虽非异端。而其害有甚于异端。其陋远下于事功。而其害终至于丧邦。虽一世之所谓大宗师及一二巨儒。亦仅能端靖自守而已。亦不敢出一言发一议。恢张正道。痛袪此弊。乃至使一废疾沈伏。五十无闻之一穷儒。潜居屏处。隐忧深叹。徒自仰屋。无所告诉。时逢亲知。辄不免呶呶半饷。而人微地轻。言不见重。终不免抑塞无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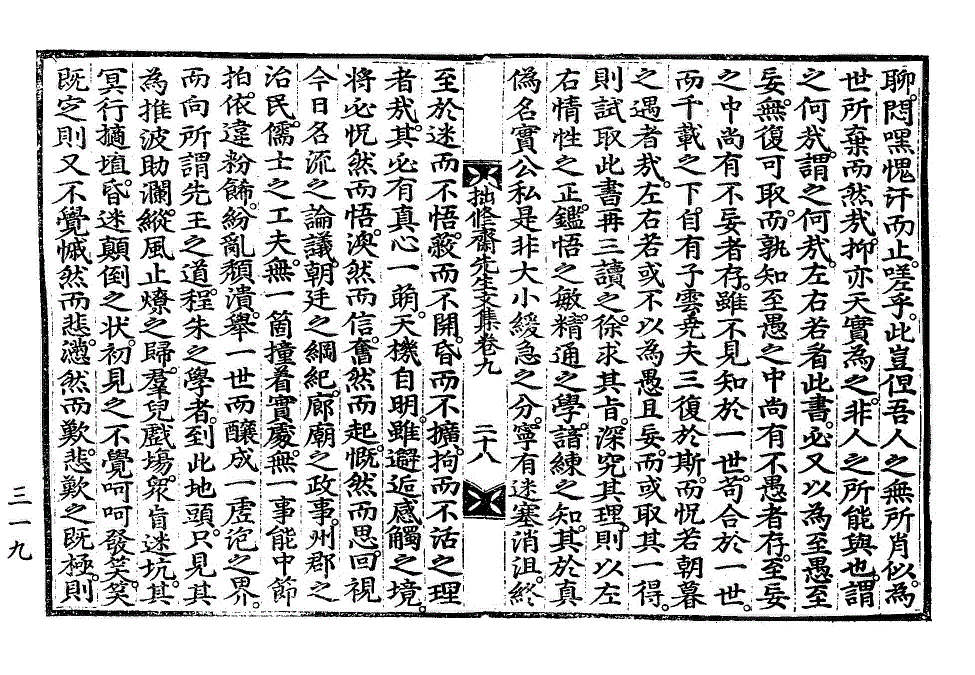 聊。闷嘿愧汗而止。嗟乎。此岂但吾人之无所肖似。为世所弃而然哉。抑亦天实为之。非人之所能与也。谓之何哉。谓之何哉。左右若看此书。必又以为至愚至妄。无复可取。而孰知至愚之中尚有不愚者存。至妄之中尚有不妄者存。虽不见知于一世。苟合于一世。而千载之下。自有子云,尧夫三复于斯。而恍若朝暮之遇者哉。左右若或不以为愚且妄。而或取其一得。则试取此书再三读之。徐求其旨。深究其理。则以左右情性之正。鉴悟之敏。精通之学。谙练之知。其于真伪名实公私是非大小缓急之分。宁有迷塞消沮。终至于迷而不悟。蔽而不开。昏而不扩。拘而不活之理者哉。其必有真心一萌。天机自明。虽邂逅感触之境。将必恍然而悟。涣然而信。奋然而起。慨然而思。回视今日名流之论议。朝廷之纲纪。廊庙之政事。州郡之治民。儒士之工夫。无一个撞着实处。无一事能中节拍。依违粉饰。纷乱颓溃。举一世而酿成一虚泡之界。而向所谓先王之道。程朱之学者。到此地头。只见其为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之归。群儿戏场。众盲迷坑。其冥行擿埴。昏迷颠倒之状。初见之不觉呵呵发笑。笑既定则又不觉戚然而悲。懑然而叹。悲叹之既极。则
聊。闷嘿愧汗而止。嗟乎。此岂但吾人之无所肖似。为世所弃而然哉。抑亦天实为之。非人之所能与也。谓之何哉。谓之何哉。左右若看此书。必又以为至愚至妄。无复可取。而孰知至愚之中尚有不愚者存。至妄之中尚有不妄者存。虽不见知于一世。苟合于一世。而千载之下。自有子云,尧夫三复于斯。而恍若朝暮之遇者哉。左右若或不以为愚且妄。而或取其一得。则试取此书再三读之。徐求其旨。深究其理。则以左右情性之正。鉴悟之敏。精通之学。谙练之知。其于真伪名实公私是非大小缓急之分。宁有迷塞消沮。终至于迷而不悟。蔽而不开。昏而不扩。拘而不活之理者哉。其必有真心一萌。天机自明。虽邂逅感触之境。将必恍然而悟。涣然而信。奋然而起。慨然而思。回视今日名流之论议。朝廷之纲纪。廊庙之政事。州郡之治民。儒士之工夫。无一个撞着实处。无一事能中节拍。依违粉饰。纷乱颓溃。举一世而酿成一虚泡之界。而向所谓先王之道。程朱之学者。到此地头。只见其为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之归。群儿戏场。众盲迷坑。其冥行擿埴。昏迷颠倒之状。初见之不觉呵呵发笑。笑既定则又不觉戚然而悲。懑然而叹。悲叹之既极。则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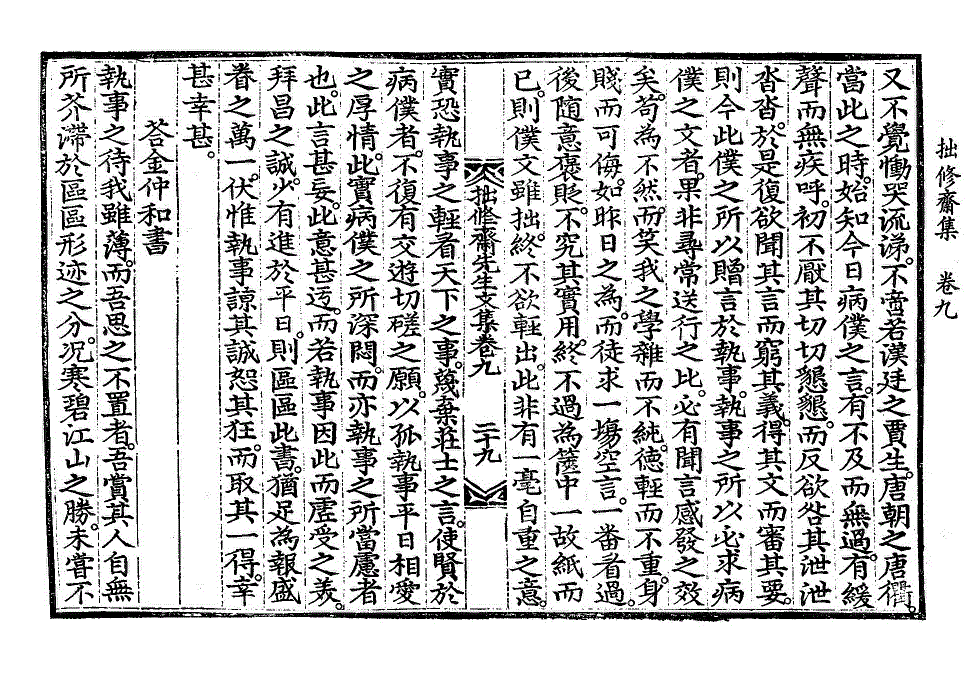 又不觉恸哭流涕。不啻若汉廷之贾生。唐朝之唐衢。当此之时。始知今日病仆之言。有不及而无过。有缓声而无疾呼。初不厌其切切恳恳。而反欲咎其泄泄沓沓。于是复欲闻其言而穷其义。得其文而审其要。则今此仆之所以赠言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必求病仆之文者。果非寻常送行之比。必有闻言感发之效矣。苟为不然。而笑我之学杂而不纯。德轻而不重。身贱而可侮。如昨日之为。而徒求一场空言。一番看过。后随意褒贬。不究其实用。终不过为箧中一故纸而已。则仆文虽拙。终不欲轻出。此非有一毫自重之意。实恐执事之轻看天下之事。蔑弃庄士之言。使贤于病仆者。不复有交游切磋之愿。以孤执事平日相爱之厚情。此实病仆之所深闷。而亦执事之所当虑者也。此言甚妄。此意甚迂。而若执事因此而虚受之美。拜昌之诚。少有进于平日。则区区此书。犹足为报盛眷之万一。伏惟执事谅其诚恕其狂。而取其一得。幸甚幸甚。
又不觉恸哭流涕。不啻若汉廷之贾生。唐朝之唐衢。当此之时。始知今日病仆之言。有不及而无过。有缓声而无疾呼。初不厌其切切恳恳。而反欲咎其泄泄沓沓。于是复欲闻其言而穷其义。得其文而审其要。则今此仆之所以赠言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必求病仆之文者。果非寻常送行之比。必有闻言感发之效矣。苟为不然。而笑我之学杂而不纯。德轻而不重。身贱而可侮。如昨日之为。而徒求一场空言。一番看过。后随意褒贬。不究其实用。终不过为箧中一故纸而已。则仆文虽拙。终不欲轻出。此非有一毫自重之意。实恐执事之轻看天下之事。蔑弃庄士之言。使贤于病仆者。不复有交游切磋之愿。以孤执事平日相爱之厚情。此实病仆之所深闷。而亦执事之所当虑者也。此言甚妄。此意甚迂。而若执事因此而虚受之美。拜昌之诚。少有进于平日。则区区此书。犹足为报盛眷之万一。伏惟执事谅其诚恕其狂。而取其一得。幸甚幸甚。答金仲和书
执事之待我虽薄。而吾思之不置者。吾赏其人自无所芥滞于区区形迹之分。况寒碧江山之胜。未尝不
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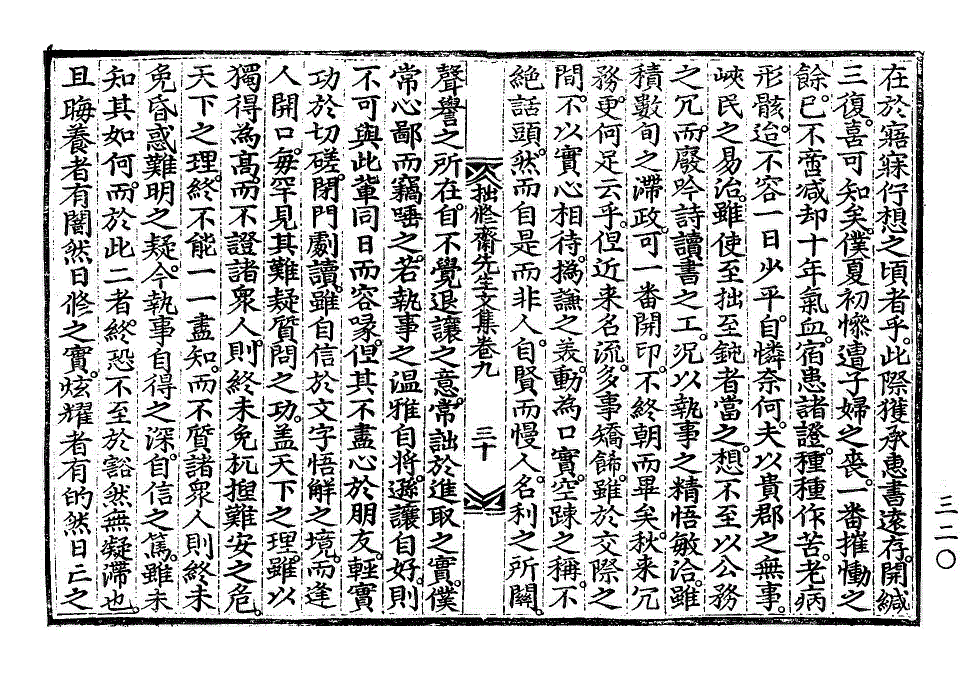 在于寤寐伫想之顷者乎。此际获承惠书远存。开缄三复。喜可知矣。仆夏初惨遭子妇之丧。一番摧恸之馀。已不啻减却十年气血。宿患诸證。种种作苦。老病形骸。迨不容一日少平。自怜奈何。夫以贵郡之无事。峡民之易治。虽使至拙至钝者当之。想不至以公务之冗。而废吟诗读书之工。况以执事之精悟敏洽。虽积数旬之滞政。可一番开印。不终朝而毕矣。秋来冗务。更何足云乎。但近来名流。多事矫饰。虽于交际之间。不以实心相待。撝谦之美。动为口实。空疏之称。不绝话头。然而自是而非人。自贤而慢人。名利之所关。声誉之所在。自不觉退让之意。常诎于进取之实。仆常心鄙而窃唾之。若执事之温雅自将。逊让自好。则不可与此辈同日而容喙。但其不尽心于朋友。轻实功于切磋。闭门剧读。虽自信于文字悟解之境。而逢人开口。每罕见其难疑质问之功。盖天下之理。虽以独得为高。而不證诸众人。则终未免杌捏(一作隉)难安之危。天下之理。终不能一一尽知。而不质诸众人则终未免昏惑难明之疑。今执事自得之深。自信之笃。虽未知其如何。而于此二者。终恐不至于豁然无凝滞也。且晦养者有闇然日修之实。炫耀者有的然日亡之
在于寤寐伫想之顷者乎。此际获承惠书远存。开缄三复。喜可知矣。仆夏初惨遭子妇之丧。一番摧恸之馀。已不啻减却十年气血。宿患诸證。种种作苦。老病形骸。迨不容一日少平。自怜奈何。夫以贵郡之无事。峡民之易治。虽使至拙至钝者当之。想不至以公务之冗。而废吟诗读书之工。况以执事之精悟敏洽。虽积数旬之滞政。可一番开印。不终朝而毕矣。秋来冗务。更何足云乎。但近来名流。多事矫饰。虽于交际之间。不以实心相待。撝谦之美。动为口实。空疏之称。不绝话头。然而自是而非人。自贤而慢人。名利之所关。声誉之所在。自不觉退让之意。常诎于进取之实。仆常心鄙而窃唾之。若执事之温雅自将。逊让自好。则不可与此辈同日而容喙。但其不尽心于朋友。轻实功于切磋。闭门剧读。虽自信于文字悟解之境。而逢人开口。每罕见其难疑质问之功。盖天下之理。虽以独得为高。而不證诸众人。则终未免杌捏(一作隉)难安之危。天下之理。终不能一一尽知。而不质诸众人则终未免昏惑难明之疑。今执事自得之深。自信之笃。虽未知其如何。而于此二者。终恐不至于豁然无凝滞也。且晦养者有闇然日修之实。炫耀者有的然日亡之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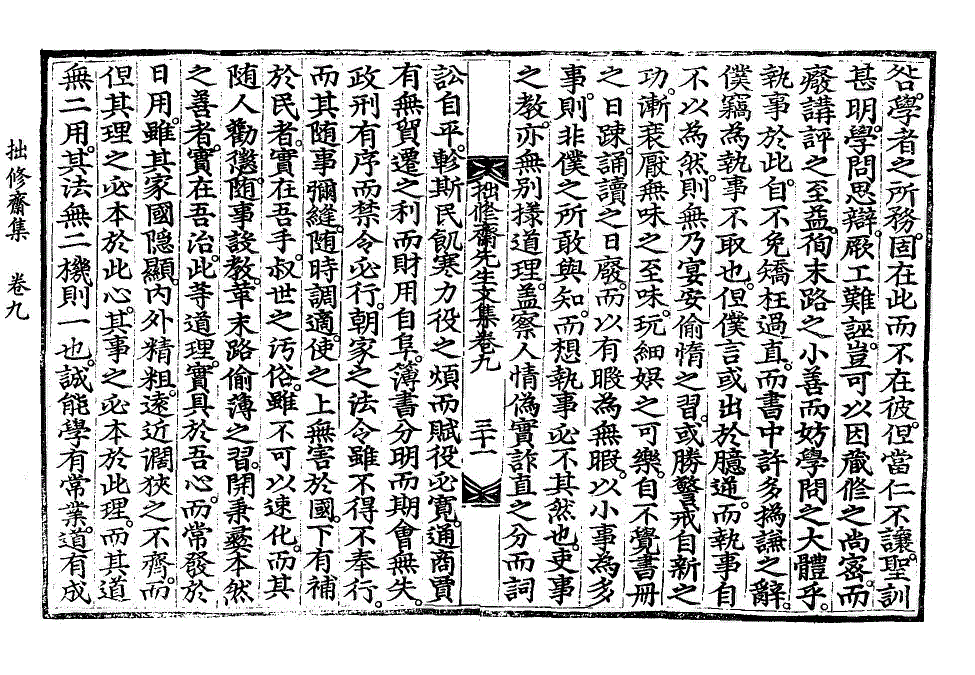 咎。学者之所务。固在此而不在彼。但当仁不让。圣训甚明。学问思辩。厥工难诬。岂可以因藏修之尚密。而癈讲评之至益。徇末路之小善而妨学问之大体乎。执事于此。自不免矫枉过直。而书中许多撝谦之辞。仆窃为执事不取也。但仆言或出于臆逆。而执事自不以为然。则无乃宴安偷惰之习。或胜警戒自新之功。渐衰厌无味之至味。玩细娱之可乐。自不觉书册之日疏。诵读之日废。而以有暇为无暇。以小事为多事。则非仆之所敢与知。而想执事必不其然也。吏事之教。亦无别样道理。盖察人情伪实诈直之分而词讼自平。轸斯民饥寒力役之烦而赋役必宽。通商贾有无贸迁之利而财用自阜。簿书分明而期会无失。政刑有序而禁令必行。朝家之法令虽不得不奉行。而其随事弥缝。随时调适。使之上无害于国。下有补于民者。实在吾手。叔世之污俗。虽不可以速化。而其随人劝惩。随事设教。革末路偷薄之习。开秉彝本然之善者。实在吾治。此等道理。实具于吾心。而常发于日用。虽其家国隐显。内外精粗。远近阔狭之不齐。而但其理之必本于此心。其事之必本于此理。而其道无二用。其法无二机则一也。诚能学有常业。道有成
咎。学者之所务。固在此而不在彼。但当仁不让。圣训甚明。学问思辩。厥工难诬。岂可以因藏修之尚密。而癈讲评之至益。徇末路之小善而妨学问之大体乎。执事于此。自不免矫枉过直。而书中许多撝谦之辞。仆窃为执事不取也。但仆言或出于臆逆。而执事自不以为然。则无乃宴安偷惰之习。或胜警戒自新之功。渐衰厌无味之至味。玩细娱之可乐。自不觉书册之日疏。诵读之日废。而以有暇为无暇。以小事为多事。则非仆之所敢与知。而想执事必不其然也。吏事之教。亦无别样道理。盖察人情伪实诈直之分而词讼自平。轸斯民饥寒力役之烦而赋役必宽。通商贾有无贸迁之利而财用自阜。簿书分明而期会无失。政刑有序而禁令必行。朝家之法令虽不得不奉行。而其随事弥缝。随时调适。使之上无害于国。下有补于民者。实在吾手。叔世之污俗。虽不可以速化。而其随人劝惩。随事设教。革末路偷薄之习。开秉彝本然之善者。实在吾治。此等道理。实具于吾心。而常发于日用。虽其家国隐显。内外精粗。远近阔狭之不齐。而但其理之必本于此心。其事之必本于此理。而其道无二用。其法无二机则一也。诚能学有常业。道有成拙修斋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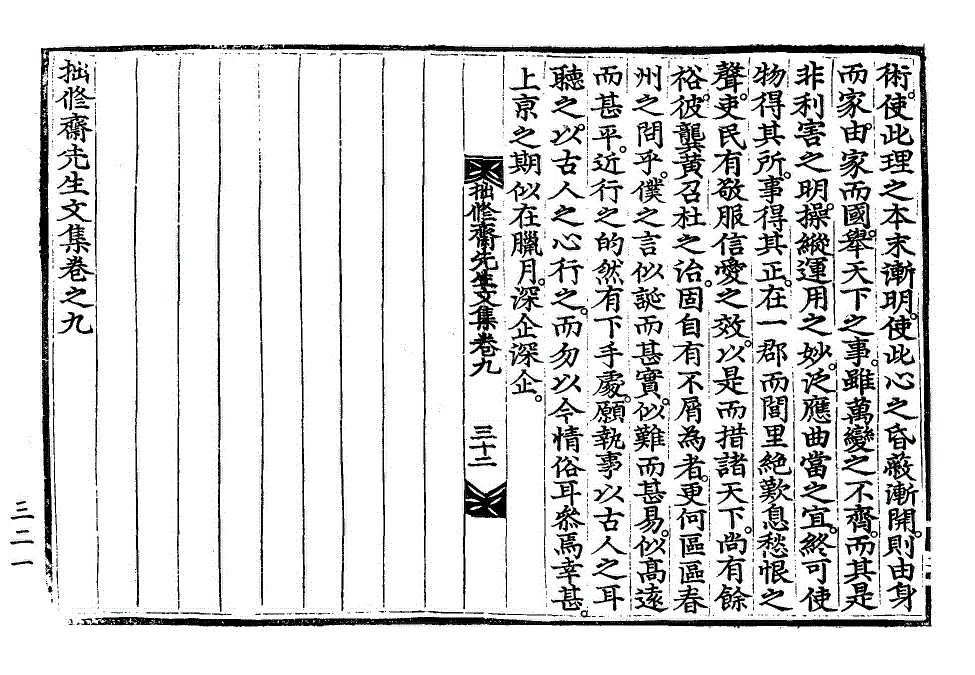 术。使此理之本末渐明。使此心之昏蔽渐开。则由身而家。由家而国。举天下之事。虽万变之不齐。而其是非利害之明。操纵运用之妙。泛应曲当之宜。终可使物得其所。事得其正。在一郡而闾里绝叹息愁恨之声。吏民有敬服信爱之效。以是而措诸天下。尚有馀裕。彼龚黄召杜之治。固自有不屑为者。更何区区春州之问乎。仆之言似诞而甚实。似难而甚易。似高远而甚平。近行之的然有下手处。愿执事以古人之耳听之。以古人之心行之。而勿以今情俗耳参焉幸甚。上京之期似在腊月。深企深企。
术。使此理之本末渐明。使此心之昏蔽渐开。则由身而家。由家而国。举天下之事。虽万变之不齐。而其是非利害之明。操纵运用之妙。泛应曲当之宜。终可使物得其所。事得其正。在一郡而闾里绝叹息愁恨之声。吏民有敬服信爱之效。以是而措诸天下。尚有馀裕。彼龚黄召杜之治。固自有不屑为者。更何区区春州之问乎。仆之言似诞而甚实。似难而甚易。似高远而甚平。近行之的然有下手处。愿执事以古人之耳听之。以古人之心行之。而勿以今情俗耳参焉幸甚。上京之期似在腊月。深企深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