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x 页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书
书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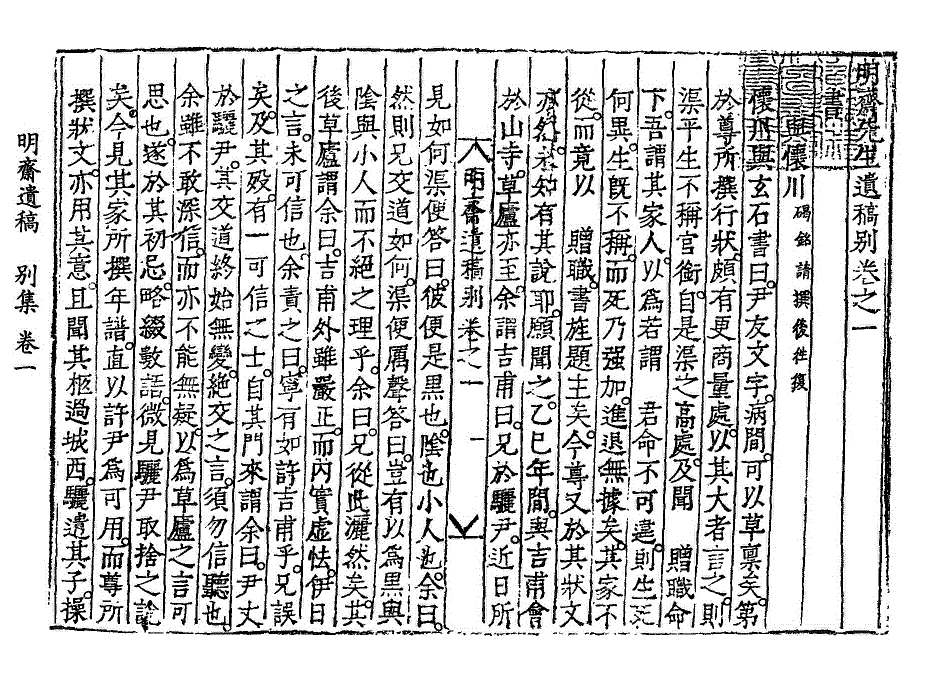 与怀川(碣铭请撰后往复)
与怀川(碣铭请撰后往复)怀川与玄石书曰。尹友文字。病间。可以草禀矣。第于尊所撰行状。颇有更商量处。以其大者言之。则渠平生不称官衔。自是渠之高处。及闻 赠职命下。吾谓其家人。以为若谓 君命不可违。则生死何异。生既不称。而死乃强加。进退无据矣。其家不从。而竟以 赠职。书旌题主矣。今尊又于其状文亦然。未知有其说耶。愿闻之。乙巳年间。与吉甫会于山寺。草庐亦至。余谓吉甫曰。兄于骊尹。近日所见如何。渠便答曰。彼便是黑也。阴也小人也。余曰。然则兄交道如何。渠便厉声答曰。岂有以为黑与阴与小人而不绝之理乎。余曰。兄从此洒然矣。其后草庐谓余曰。吉甫外虽严正。而内实虚怯。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责之曰。宁有如许吉甫乎。兄误矣。及其殁。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门来谓余曰。尹丈于骊尹。其交道终始无变。绝交之言。须勿信听也。余虽不敢深信。而亦不能无疑。以为草庐之言可思也。遂于其初忌。略缀数语。微见骊尹取舍之说矣。今见其家所撰年谱。直以许尹为可用。而尊所撰状文。亦用其意。且闻其柩过城西。骊遣其子。操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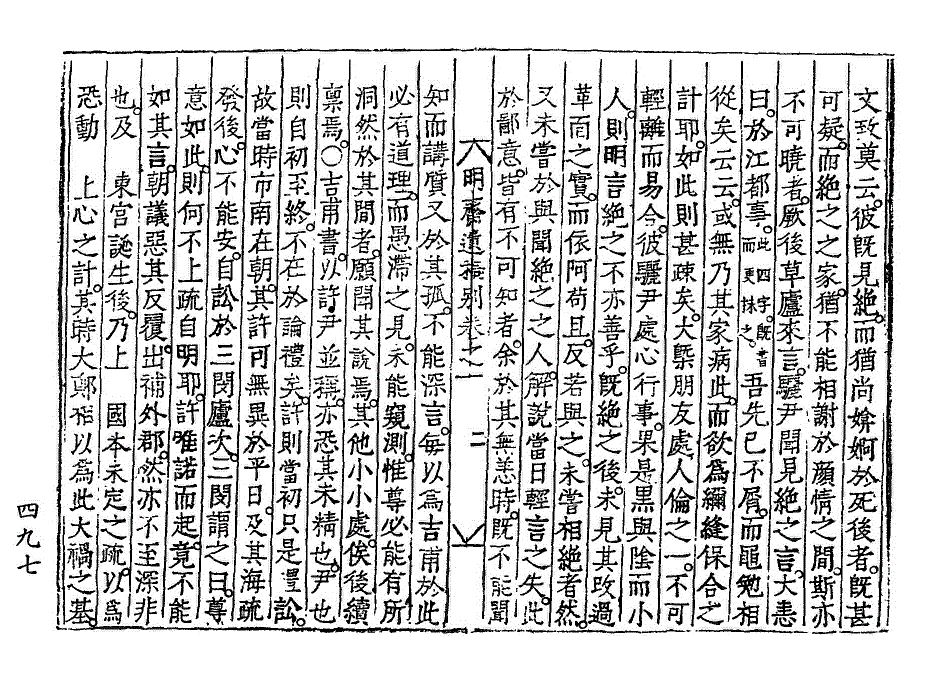 文致莫云。彼既见绝。而犹尚媕婀于死后者。既甚可疑。而绝之之家。犹不能相谢于颜情之间。斯亦不可晓者。厥后草庐来言。骊尹闻见绝之言。大恚曰。于江都事。(此四字。既书而更抹之。)吾先已不屑。而黾勉相从矣云云。或无乃其家病此。而欲为䌤缝保合之计耶。如此则甚疏矣。大槩朋友处人伦之一。不可轻离而易合。彼骊尹处心行事。果是黑与阴而小人。则明言绝之不亦善乎。既绝之后。未见其改过革面之实。而依阿苟且。反若与之。未尝相绝者然。又未尝于与闻绝之之人。解说当日轻言之失。此于鄙意。皆有不可知者。余于其无恙时。既不能闻知而讲质又于其孤。不能深言。每以为吉甫于此必有道理。而愚滞之见。未能窥测。惟尊必能有所洞然于其间者。愿闻其说焉。其他小小处。俟后续禀焉。○吉甫书。以许,尹并称。亦恐其未精也。尹也则自初至终。不在于论礼矣。许则当初只是禯讼。故当时市南在朝。其许可无异于平日。及其海疏发后。心不能安。自讼于三闵庐次。三闵谓之曰。尊意如此。则何不上疏自明耶。许唯诺而起。竟不能如其言。朝议恶其反覆。出补外郡。然亦不至深非也。及 东宫诞生后。乃上 国本未定之疏。以为恐动 上心之计。其时大郑相以为此大祸之基。
文致莫云。彼既见绝。而犹尚媕婀于死后者。既甚可疑。而绝之之家。犹不能相谢于颜情之间。斯亦不可晓者。厥后草庐来言。骊尹闻见绝之言。大恚曰。于江都事。(此四字。既书而更抹之。)吾先已不屑。而黾勉相从矣云云。或无乃其家病此。而欲为䌤缝保合之计耶。如此则甚疏矣。大槩朋友处人伦之一。不可轻离而易合。彼骊尹处心行事。果是黑与阴而小人。则明言绝之不亦善乎。既绝之后。未见其改过革面之实。而依阿苟且。反若与之。未尝相绝者然。又未尝于与闻绝之之人。解说当日轻言之失。此于鄙意。皆有不可知者。余于其无恙时。既不能闻知而讲质又于其孤。不能深言。每以为吉甫于此必有道理。而愚滞之见。未能窥测。惟尊必能有所洞然于其间者。愿闻其说焉。其他小小处。俟后续禀焉。○吉甫书。以许,尹并称。亦恐其未精也。尹也则自初至终。不在于论礼矣。许则当初只是禯讼。故当时市南在朝。其许可无异于平日。及其海疏发后。心不能安。自讼于三闵庐次。三闵谓之曰。尊意如此。则何不上疏自明耶。许唯诺而起。竟不能如其言。朝议恶其反覆。出补外郡。然亦不至深非也。及 东宫诞生后。乃上 国本未定之疏。以为恐动 上心之计。其时大郑相以为此大祸之基。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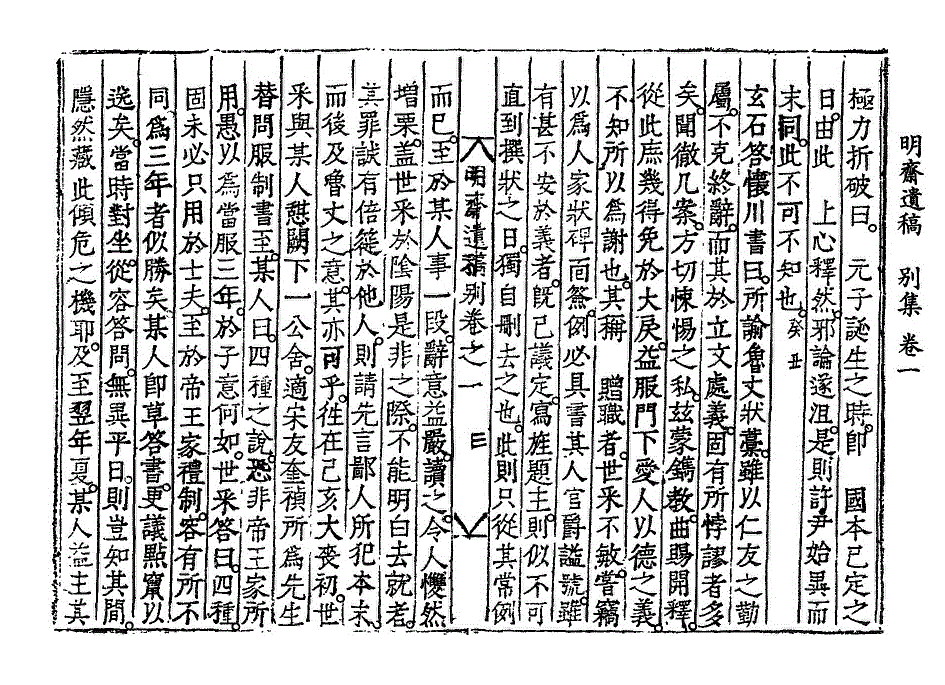 极力折破曰。 元子诞生之时。即 国本已定之日。由此 上心释然。邪论遂沮。是则许尹始异而末同。此不可不知也。(癸丑)
极力折破曰。 元子诞生之时。即 国本已定之日。由此 上心释然。邪论遂沮。是则许尹始异而末同。此不可不知也。(癸丑)玄石答怀川书曰。所谕鲁丈状稿。虽以仁友之勤属。不克终辞。而其于立文处义。固有所悖谬者多矣。闻彻几案。方切悚惕之私。玆蒙镌教。曲赐开释。从此庶几得免于大戾。益服门下爱人以德之义。不知所以为谢也。其称 赠职者。世采不敏。尝窃以为人家状碑面签。例必具书其人官爵谥号。虽有甚不安于义者。既已议定。写旌题主。则似不可直到撰状之日。独自删去之也。此则只从其常例而已。至于某人事一段。辞意益严。读之。令人㩳然增栗。盖世采于阴阳是非之际。不能明白去就者。其罪诚有倍筛于他人。则请先言鄙人所犯本末。而后及鲁丈之意。其亦可乎。往在己亥大丧初。世采与某人憩阙下一公舍。适宋友奎祯所为先生替问服制书至。某人曰。四种之说。恐非帝王家所用。愚以为当服三年。于子意何如。世采答曰。四种。固未必只用于士夫。至于帝王家礼制。容有所不同为三年者似胜矣。某人即草答书。更议点窜以送矣。当时对坐。从容答问。无异平日。则岂知其间。隐然藏此倾危之机耶。及至翌年夏。某人益主其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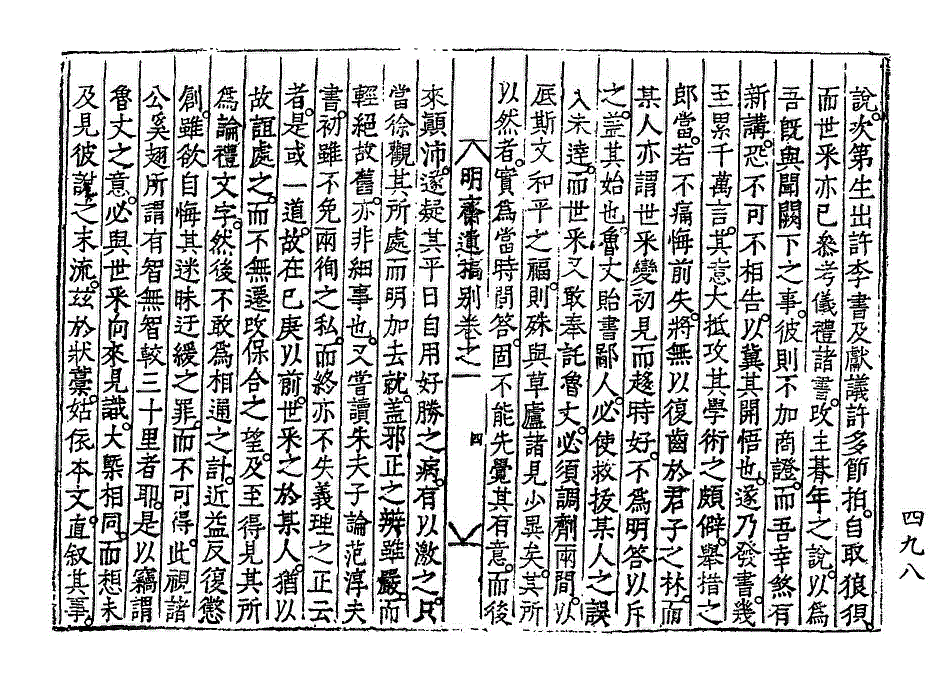 说。次第生出许李书及献议许多节拍。自取狼狈。而世采亦已参考仪礼诸书。改主期年之说。以为吾既与闻阙下之事。彼则不加商證。而吾幸杀有新讲。恐不可不相告。以冀其开悟也。遂乃发书。几至累千万言。其意大抵攻其学术之颇僻。举措之郎当。若不痛悔前失。将无以复齿于君子之林。而某人亦谓世采变初见而趍时好。不为明答以斥之。盖其始也。鲁丈贻书鄙人。必使救拔某人之误入未达。而世采又敢奉托鲁丈。必须调剂两间。以底斯文和平之福。则殊与草庐诸见少异矣。其所以然者。实为当时问答。固不能先觉其有意。而后来颠沛。遂疑其平日自用好胜之病。有以激之。只当徐观其所处而明加去就。盖邪正之辨虽严。而轻绝故旧。亦非细事也。又尝读朱夫子论范淳夫书。初虽不免两徇之私。而终亦不失义理之正云者。是或一道。故在己庚以前。世采之于某人。犹以故谊处之。而不无迁改保合之望。及至得见其所为论礼文字。然后不敢为相通之计。近益反复惩创。虽欲自悔其迷昧迂缓之罪。而不可得。此视诸公奚翅所谓有智无智较三十里者耶。是以窃谓鲁丈之意。必与世采向来见识。大槩相同。而想未及见彼说之末流。玆于状稿。姑依本文。直叙其事。
说。次第生出许李书及献议许多节拍。自取狼狈。而世采亦已参考仪礼诸书。改主期年之说。以为吾既与闻阙下之事。彼则不加商證。而吾幸杀有新讲。恐不可不相告。以冀其开悟也。遂乃发书。几至累千万言。其意大抵攻其学术之颇僻。举措之郎当。若不痛悔前失。将无以复齿于君子之林。而某人亦谓世采变初见而趍时好。不为明答以斥之。盖其始也。鲁丈贻书鄙人。必使救拔某人之误入未达。而世采又敢奉托鲁丈。必须调剂两间。以底斯文和平之福。则殊与草庐诸见少异矣。其所以然者。实为当时问答。固不能先觉其有意。而后来颠沛。遂疑其平日自用好胜之病。有以激之。只当徐观其所处而明加去就。盖邪正之辨虽严。而轻绝故旧。亦非细事也。又尝读朱夫子论范淳夫书。初虽不免两徇之私。而终亦不失义理之正云者。是或一道。故在己庚以前。世采之于某人。犹以故谊处之。而不无迁改保合之望。及至得见其所为论礼文字。然后不敢为相通之计。近益反复惩创。虽欲自悔其迷昧迂缓之罪。而不可得。此视诸公奚翅所谓有智无智较三十里者耶。是以窃谓鲁丈之意。必与世采向来见识。大槩相同。而想未及见彼说之末流。玆于状稿。姑依本文。直叙其事。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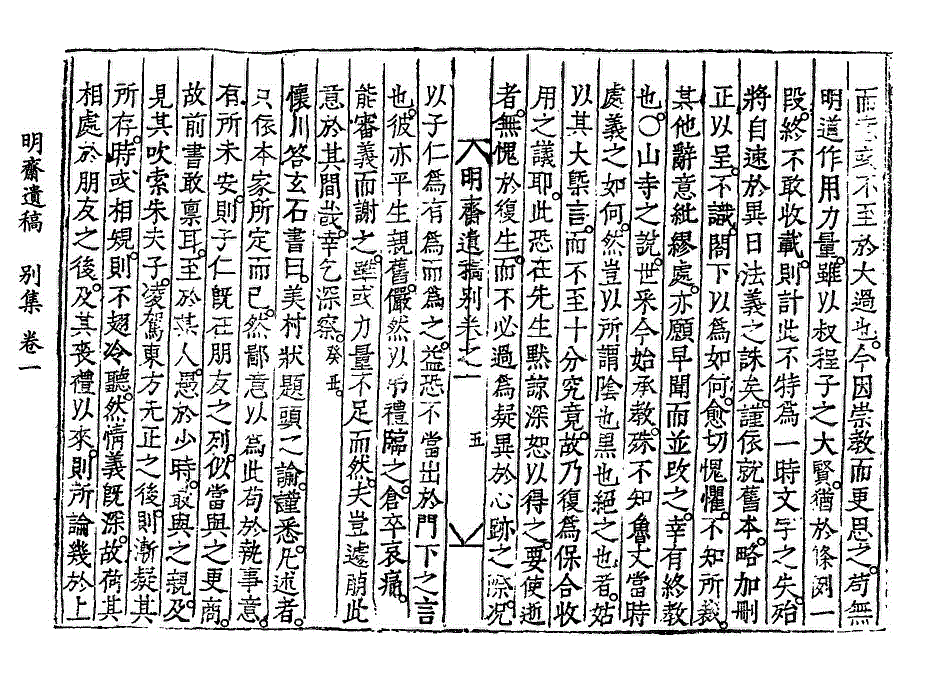 而意或不至于大过也。今因崇教而更思之。苟无明道作用力量。虽以叔程子之大贤。犹于条例一段。终不敢收载。则计此不特为一时文字之失。殆将自速于异日法义之诛矣。谨依就旧本。略加删正以呈。不识。閤下以为如何。愈切愧惧。不知所裁。其他辞意纰缪处。亦愿早闻而并改之。幸有终教也。○山寺之说。世采今始承教。殊不知鲁丈当时处义之如何。然岂以所谓阴也黑也绝之也者。姑以其大槩言。而不至十分究竟。故乃复为保合收用之议耶。此恐在先生默谅深恕以得之。要使逝者。无愧于复生。而不必过为疑异于心迹之际。况以子仁为有为而为之。益恐不当出于门下之言也。彼亦平生亲旧。俨然以吊礼临之。仓卒哀痛。能审义而谢之。虽或力量不足而然。夫岂遽萌此意于其间哉。幸乞深察。(癸丑。)
而意或不至于大过也。今因崇教而更思之。苟无明道作用力量。虽以叔程子之大贤。犹于条例一段。终不敢收载。则计此不特为一时文字之失。殆将自速于异日法义之诛矣。谨依就旧本。略加删正以呈。不识。閤下以为如何。愈切愧惧。不知所裁。其他辞意纰缪处。亦愿早闻而并改之。幸有终教也。○山寺之说。世采今始承教。殊不知鲁丈当时处义之如何。然岂以所谓阴也黑也绝之也者。姑以其大槩言。而不至十分究竟。故乃复为保合收用之议耶。此恐在先生默谅深恕以得之。要使逝者。无愧于复生。而不必过为疑异于心迹之际。况以子仁为有为而为之。益恐不当出于门下之言也。彼亦平生亲旧。俨然以吊礼临之。仓卒哀痛。能审义而谢之。虽或力量不足而然。夫岂遽萌此意于其间哉。幸乞深察。(癸丑。)怀川答玄石书曰。美村状题头之谕。谨悉。凡述者。只依本家所定而已。然鄙意以为此苟于执事意。有所未安。则子仁既在朋友之列。似当与之更商。故前书敢禀耳。至于某人。愚于少时。最与之亲。及见其吹索朱夫子。凌驾东方先正之后。则渐疑其所存。时或相规。则不翅冷听。然情义既深。故荷其相处于朋友之后。及其丧礼以来。则所论几于上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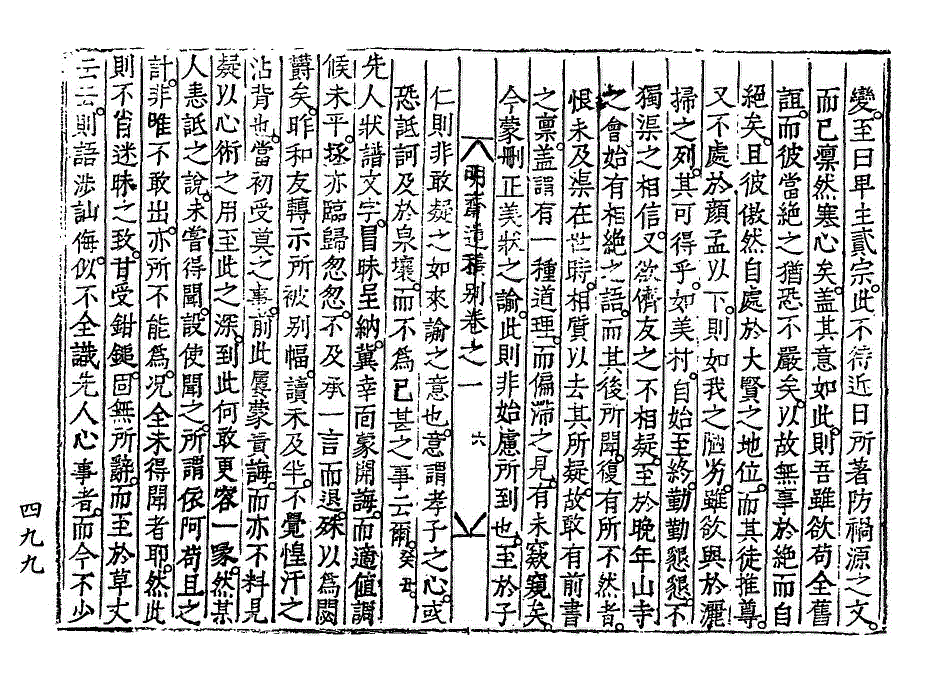 变。至曰卑主贰宗。此不待近日所著防祸源之文。而已凛然寒心矣。盖其意如此。则吾虽欲苟全旧谊。而彼当绝之犹恐不严矣。以故无事于绝而自绝矣。且彼傲然自处于大贤之地位。而其徒推尊。又不处于颜孟以下。则如我之陋劣。虽欲与于洒扫之列。其可得乎。如美村。自始至终。勤勤恳恳。不独渠之相信。又欲侪友之不相疑。至于晚年山寺之会。始有相绝之语。而其后所闻。复有所不然者。恨未及渠在世时。相质以去其所疑。故敢有前书之禀。盖谓有一种道理。而偏滞之见。有未窾窥矣。今蒙删正美状之谕。此则非始虑所到也。至于子仁则非敢疑之如来谕之意也。意谓孝子之心。或恐诋诃及于泉壤。而不为已甚之事云尔。(癸丑。)
变。至曰卑主贰宗。此不待近日所著防祸源之文。而已凛然寒心矣。盖其意如此。则吾虽欲苟全旧谊。而彼当绝之犹恐不严矣。以故无事于绝而自绝矣。且彼傲然自处于大贤之地位。而其徒推尊。又不处于颜孟以下。则如我之陋劣。虽欲与于洒扫之列。其可得乎。如美村。自始至终。勤勤恳恳。不独渠之相信。又欲侪友之不相疑。至于晚年山寺之会。始有相绝之语。而其后所闻。复有所不然者。恨未及渠在世时。相质以去其所疑。故敢有前书之禀。盖谓有一种道理。而偏滞之见。有未窾窥矣。今蒙删正美状之谕。此则非始虑所到也。至于子仁则非敢疑之如来谕之意也。意谓孝子之心。或恐诋诃及于泉壤。而不为已甚之事云尔。(癸丑。)先人状谱文字。冒昧呈纳。冀幸面蒙开诲。而适值调候未平。拯亦临归悤忽。不及承一言而退。殊以为閟郁矣。昨和友转示所被别幅。读未及半。不觉惶汗之沾背也。当初受준奠之事。前此屡蒙责诲。而亦不料见疑以心术之用至此之深。到此何敢更容一喙。然某人恚诋之说。未尝得闻。设使闻之。所谓依阿苟且之计。非唯不敢出。亦所不能为。况全未得闻者耶。然此则不肖迷昧之致。甘受钳锤。固无所辞。而至于草丈云云。则语涉讪侮。似不全识先人心事者。而今不少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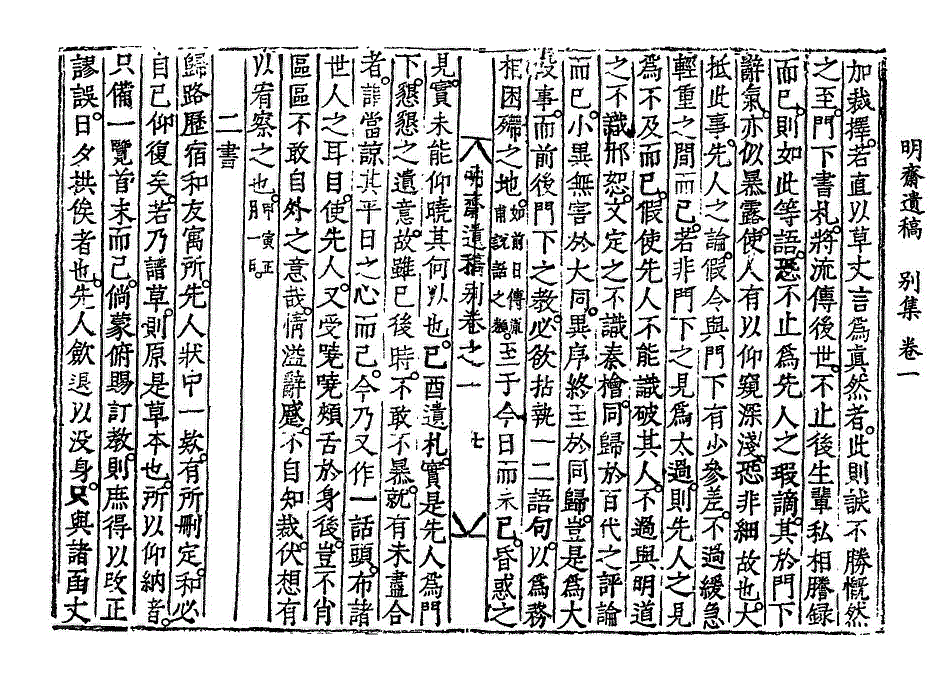 加裁择。若直以草丈言为真然者。此则诚不胜慨然之至。门下书札。将流传后世。不止后生辈私相誊录而已。则如此等语。恐不止为先人之瑕谪。其于门下辞气。亦似暴露。使人有以仰窥深浅。恐非细故也。大抵此事。先人之论。假令与门下有少参差。不过缓急轻重之间而已。若非门下之见为太过。则先人之见为不及而已。假使先人不能识破其人。不过与明道之不识邢恕。文定之不识秦桧。同归于百代之评论而已。小异无害于大同。异序终至于同归。岂是为大段事。而前后门下之教。必欲拈执一二语句。以为务相困殢之地。(如前日传胤甫说话之类。)至于今日而未已。昏惑之见。实未能仰晓其何以也。己酉遗札。实是先人为门下。恳恳之遗意。故虽已后时。不敢不暴。就有未尽合者。谓当谅其平日之心而已。今乃又作一话头。布诸世人之耳目。使先人。又受哓哓颊舌于身后。岂不肖区区不敢自外之意哉。情溢辞蹙。不自知裁。伏想有以宥察之也。(甲寅正月一日。)
加裁择。若直以草丈言为真然者。此则诚不胜慨然之至。门下书札。将流传后世。不止后生辈私相誊录而已。则如此等语。恐不止为先人之瑕谪。其于门下辞气。亦似暴露。使人有以仰窥深浅。恐非细故也。大抵此事。先人之论。假令与门下有少参差。不过缓急轻重之间而已。若非门下之见为太过。则先人之见为不及而已。假使先人不能识破其人。不过与明道之不识邢恕。文定之不识秦桧。同归于百代之评论而已。小异无害于大同。异序终至于同归。岂是为大段事。而前后门下之教。必欲拈执一二语句。以为务相困殢之地。(如前日传胤甫说话之类。)至于今日而未已。昏惑之见。实未能仰晓其何以也。己酉遗札。实是先人为门下。恳恳之遗意。故虽已后时。不敢不暴。就有未尽合者。谓当谅其平日之心而已。今乃又作一话头。布诸世人之耳目。使先人。又受哓哓颊舌于身后。岂不肖区区不敢自外之意哉。情溢辞蹙。不自知裁。伏想有以宥察之也。(甲寅正月一日。)与怀川[二书]
归路历宿和友寓所。先人状中一款。有所删定。和必自己仰复矣。若乃谱草。则原是草本也。所以仰纳者。只备一览首末而已。倘蒙俯赐订教。则庶得以改正谬误。日夕拱俟者也。先人敛退以没身。只与诸函丈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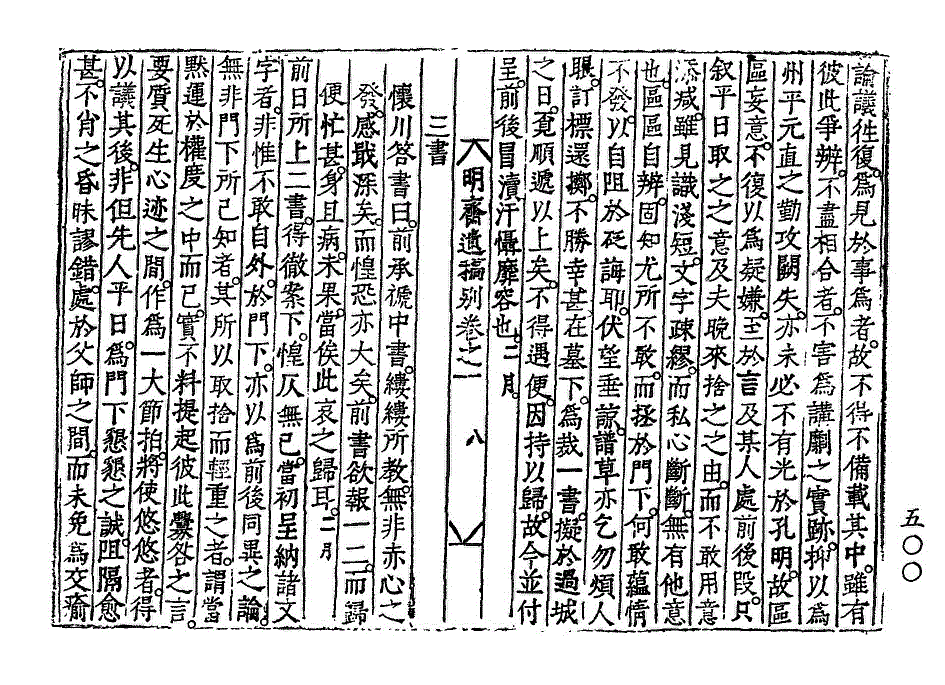 论议往复。为见于事为者。故不得不备载其中。虽有彼此争辨。不尽相合者。不害为讲劘之实迹。抑以为州平元直之勤攻阙失。亦未必不有光于孔明。故区区妄意。不复以为疑嫌。至于言及某人处前后段。只叙平日取之之意及夫晚来舍之之由。而不敢用意添减。虽见识浅短。文字疏缪。而私心断断。无有他意也。区区自辨。固知尤所不敢。而拯于门下。何敢蕴情不发。以自阻于砭诲耶。伏望垂谅。谱草亦乞勿烦人眼。订标还掷。不胜幸甚。在墓下。为裁一书。拟于过城之日。觅顺递以上矣。不得遇便。因持以归。故今并付呈。前后冒渎汗慑靡容也。(二月。)
论议往复。为见于事为者。故不得不备载其中。虽有彼此争辨。不尽相合者。不害为讲劘之实迹。抑以为州平元直之勤攻阙失。亦未必不有光于孔明。故区区妄意。不复以为疑嫌。至于言及某人处前后段。只叙平日取之之意及夫晚来舍之之由。而不敢用意添减。虽见识浅短。文字疏缪。而私心断断。无有他意也。区区自辨。固知尤所不敢。而拯于门下。何敢蕴情不发。以自阻于砭诲耶。伏望垂谅。谱草亦乞勿烦人眼。订标还掷。不胜幸甚。在墓下。为裁一书。拟于过城之日。觅顺递以上矣。不得遇便。因持以归。故今并付呈。前后冒渎汗慑靡容也。(二月。)与怀川[三书]
怀川答书曰。前承褫中书。缕缕所教。无非赤心之发。感戢深矣。而惶恐亦大矣。前书欲报一二。而归便忙甚。身且病。未果。当俟此哀之归耳。(二月)
前日所上二书。得彻案下。惶仄无已。当初呈纳诸文字者。非惟不敢自外。于门下。亦以为前后同异之论。无非门下所已知者。其所以取舍而轻重之者。谓当默运于权度之中而已。实不料提起彼此衅咎之言。要质死生心迹之间。作为一大节拍。将使悠悠者。得以议其后。非但先人平日。为门下恳恳之诚。阻隔愈甚。不肖之昏昧谬错。处于父师之间。而未免为交瘉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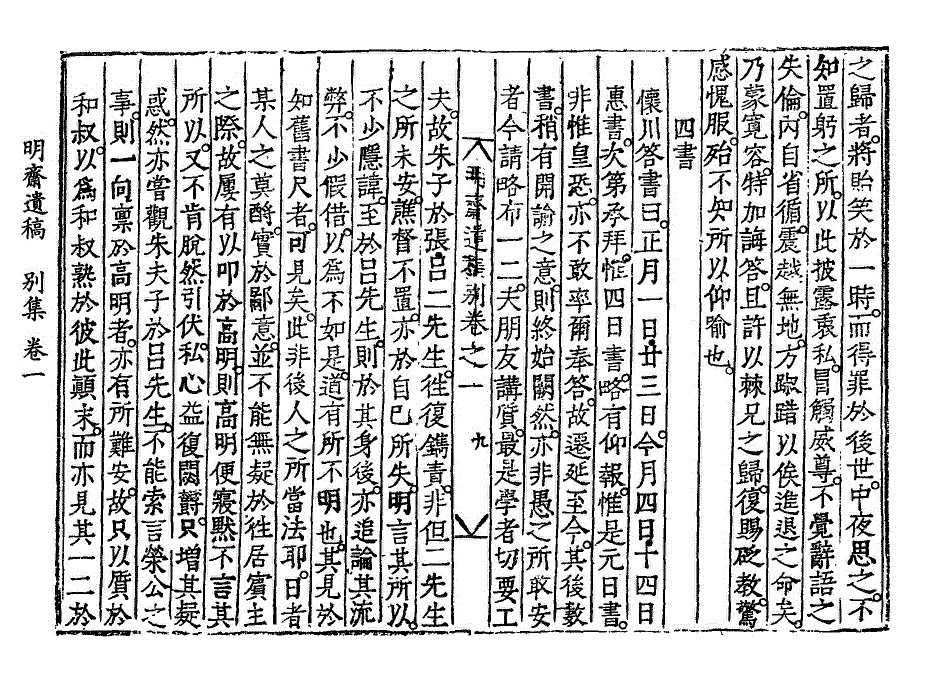 之归者。将贻笑于一时。而得罪于后世。中夜思之。不知置躬之所。以此披露衷私。冒触威尊。不觉辞语之失伦。内自省循。震越无地。方踧踖以俟进退之命矣。乃蒙宽容。特加诲答。且许以棘兄之归。复赐砭教。惊感愧服。殆不知所以仰喻也。
之归者。将贻笑于一时。而得罪于后世。中夜思之。不知置躬之所。以此披露衷私。冒触威尊。不觉辞语之失伦。内自省循。震越无地。方踧踖以俟进退之命矣。乃蒙宽容。特加诲答。且许以棘兄之归。复赐砭教。惊感愧服。殆不知所以仰喻也。与怀川[四书]
怀川答书曰。正月一日,廿三日。今月四日,十四日惠书。次第承拜。惟四日书。略有仰报。惟是元日书。非惟皇恐。亦不敢率尔奉答。故迁延至今。其后数书。稍有开谕之意。则终始阙然。亦非愚之所敢安者。今请略布一二。夫朋友讲质。最是学者切要工夫。故朱子于张,吕二先生。往复镌责。非但二先生之所未安。谯督不置。亦于自己所失。明言其所以。不少隐讳。至于吕先生。则于其身后。亦追论其流弊。不少假借。以为不如是。道有所不明也。其见于知旧书尺者。可见矣。此非后人之所当法耶。日者某人之奠酹。实于鄙意。并不能无疑于往居宾主之际。故屡有以叩于高明。则高明便寝默不言其所以。又不肯脱然引伏。私心益复閟郁。只增其疑惑。然亦尝观朱夫子于吕先生。不能索言荣公之事。则一向禀于高明者。亦有所难安。故只以质于和叔。以为和叔熟于彼此颠末。而亦见其一二于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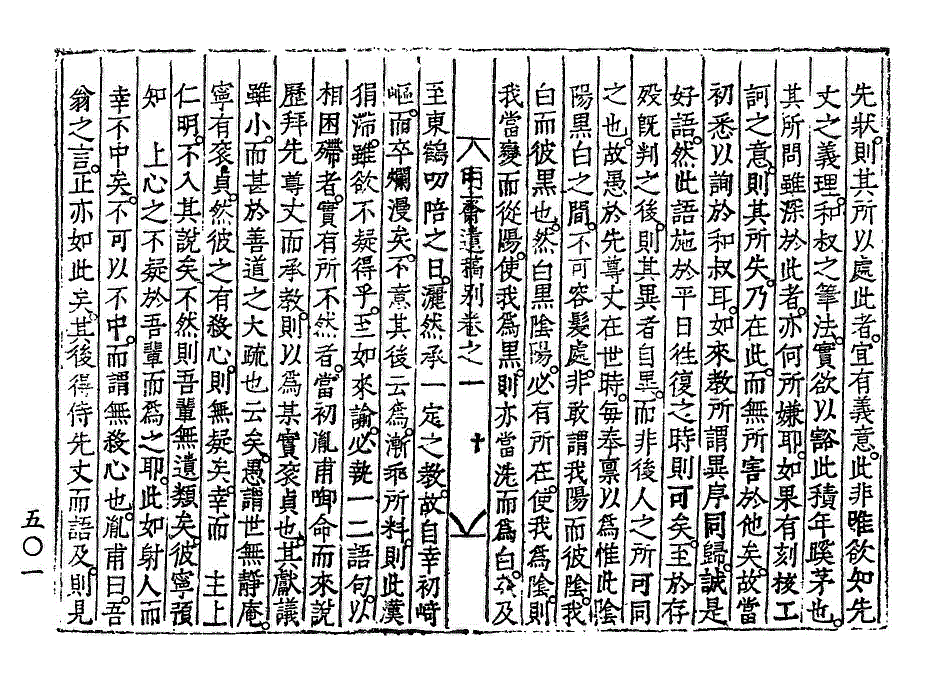 先状。则其所以处此者。宜有义意。此非唯欲知先丈之义理。和叔之笔法。实欲以豁此积年蹊茅也。其所问虽深于此者。亦何所嫌耶。如果有刻核工诃之意。则其所失。乃在此。而无所害于他矣。故当初悉以询于和叔耳。如来教所谓异序同归。诚是好语。然此语施于平日往复之时则可矣。至于存殁既判之后。则其异者自异。而非后人之所可同之也。故愚于先尊丈在世时。每奉禀以为惟此阴阳黑白之间。不可容发处。非敢谓我阳而彼阴。我白而彼黑也。然白黑阴阳。必有所在。使我为阴。则我当变而从阳。使我为黑。则亦当洗而为白矣。及至东鹤叨陪之日。洒然承一定之教。故自幸初崎岖。而卒烂漫矣。不意其后云为。渐乖所料。则此汉狷滞。虽欲不疑得乎。至如来谕。必执一二语句。以相困殢者。实有所不然者。当初胤甫衔命而来说历拜先尊丈而承教。则以为某实衮贞也。其献议虽小。而甚于善道之大疏也云矣。愚谓世无静庵。宁有衮,贞。然彼之有杀心。则无疑矣。幸而 主上仁明。不入其说矣。不然则吾辈无遗类矣。彼宁预知 上心之不疑于吾辈而为之耶。此如射人而幸不中矣。不可以不中。而谓无杀心也。胤甫曰。吾翁之言。正亦如此矣。其后得侍先丈而语及。则见
先状。则其所以处此者。宜有义意。此非唯欲知先丈之义理。和叔之笔法。实欲以豁此积年蹊茅也。其所问虽深于此者。亦何所嫌耶。如果有刻核工诃之意。则其所失。乃在此。而无所害于他矣。故当初悉以询于和叔耳。如来教所谓异序同归。诚是好语。然此语施于平日往复之时则可矣。至于存殁既判之后。则其异者自异。而非后人之所可同之也。故愚于先尊丈在世时。每奉禀以为惟此阴阳黑白之间。不可容发处。非敢谓我阳而彼阴。我白而彼黑也。然白黑阴阳。必有所在。使我为阴。则我当变而从阳。使我为黑。则亦当洗而为白矣。及至东鹤叨陪之日。洒然承一定之教。故自幸初崎岖。而卒烂漫矣。不意其后云为。渐乖所料。则此汉狷滞。虽欲不疑得乎。至如来谕。必执一二语句。以相困殢者。实有所不然者。当初胤甫衔命而来说历拜先尊丈而承教。则以为某实衮贞也。其献议虽小。而甚于善道之大疏也云矣。愚谓世无静庵。宁有衮,贞。然彼之有杀心。则无疑矣。幸而 主上仁明。不入其说矣。不然则吾辈无遗类矣。彼宁预知 上心之不疑于吾辈而为之耶。此如射人而幸不中矣。不可以不中。而谓无杀心也。胤甫曰。吾翁之言。正亦如此矣。其后得侍先丈而语及。则见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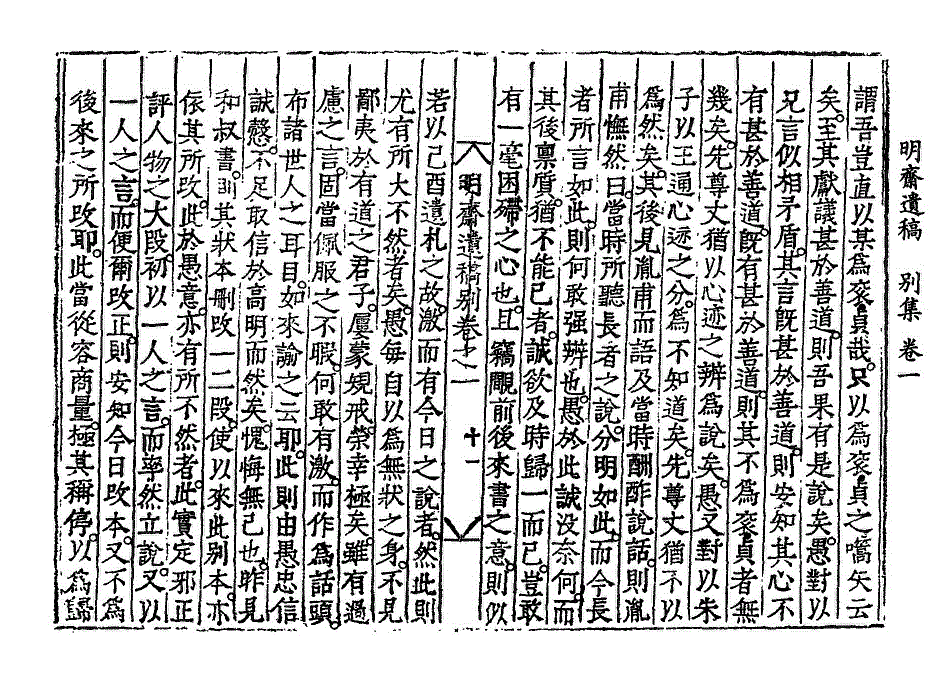 谓吾岂直以某为衮,贞哉。只以为衮,贞之嚆矢云矣。至其献议甚于善道。则吾果有是说矣。愚对以兄言似相矛盾。其言既甚于善道。则安知其心不有甚于善道。既有甚于善道。则其不为衮,贞者无几矣。先尊丈犹以心迹之辨为说矣。愚又对以朱子以王通心迹之分。为不知道矣。先尊丈犹不以为然矣。其后见胤甫而语及当时酬酢说话。则胤甫怃然曰。当时所听长者之说。分明如此。而今长者所言如此。则何敢强辨也。愚于此诚没奈何。而其后禀质。犹不能已者。诚欲及时归一而已。岂敢有一毫困殢之心也。且窃覵前后来书之意。则似若以己酉遗札之故。激而有今日之说者。然此则尤有所大不然者矣。愚每自以为无状之身。不见鄙夷于有道之君子。屡蒙规戒。荣幸极矣。虽有过虑之言。固当佩服之不暇。何敢有激。而作为话头。布诸世人之耳目。如来谕之云耶。此则由愚忠信诚悫。不足取信于高明而然矣。愧悔无已也。昨见和叔书。则其状本删改一二段。使以来此别本。亦依其所改。此于愚意。亦有所不然者。此实定邪正评人物之大段。初以一人之言。而率然立说。又以一人之言。而便尔改正。则安知今日改本。又不为后来之所改耶。此当从容商量。极其称停。以为归
谓吾岂直以某为衮,贞哉。只以为衮,贞之嚆矢云矣。至其献议甚于善道。则吾果有是说矣。愚对以兄言似相矛盾。其言既甚于善道。则安知其心不有甚于善道。既有甚于善道。则其不为衮,贞者无几矣。先尊丈犹以心迹之辨为说矣。愚又对以朱子以王通心迹之分。为不知道矣。先尊丈犹不以为然矣。其后见胤甫而语及当时酬酢说话。则胤甫怃然曰。当时所听长者之说。分明如此。而今长者所言如此。则何敢强辨也。愚于此诚没奈何。而其后禀质。犹不能已者。诚欲及时归一而已。岂敢有一毫困殢之心也。且窃覵前后来书之意。则似若以己酉遗札之故。激而有今日之说者。然此则尤有所大不然者矣。愚每自以为无状之身。不见鄙夷于有道之君子。屡蒙规戒。荣幸极矣。虽有过虑之言。固当佩服之不暇。何敢有激。而作为话头。布诸世人之耳目。如来谕之云耶。此则由愚忠信诚悫。不足取信于高明而然矣。愧悔无已也。昨见和叔书。则其状本删改一二段。使以来此别本。亦依其所改。此于愚意。亦有所不然者。此实定邪正评人物之大段。初以一人之言。而率然立说。又以一人之言。而便尔改正。则安知今日改本。又不为后来之所改耶。此当从容商量。极其称停。以为归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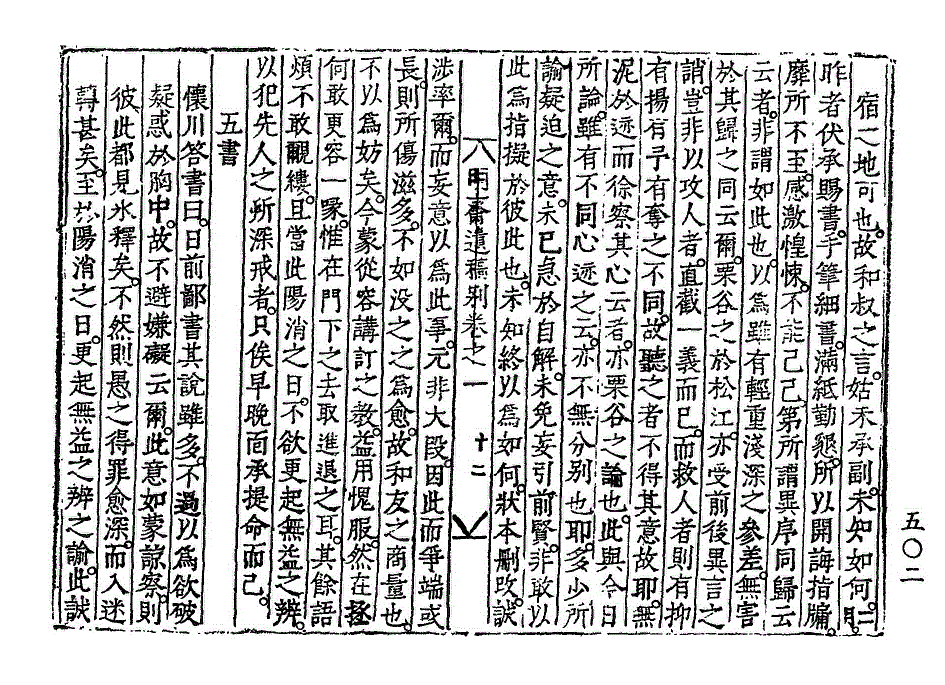 宿之地可也。故和叔之言。姑未承副。未知如何。(二月。)
宿之地可也。故和叔之言。姑未承副。未知如何。(二月。)昨者伏承赐书。手笔细书。满纸勤恳。所以开诲指牖。靡所不至。感激惶悚。不能已已。第所谓异序同归云云者。非谓如此也。以为虽有轻重浅深之参差。无害于其归之同云尔。栗谷之于松江。亦受前后异言之诮。岂非以攻人者。直截一义而已。而救人者则有抑有扬有予有夺之不同。故听之者不得其意故耶。无泥于迹而徐察其心云者。亦栗谷之论也。此与今日所论。虽有不同心迹之云。亦不无分别也耶。多少所论疑迫之意。未已急于自解。未免妄引前贤。非敢以此为指拟于彼此也。未知终以为如何。状本删改。诚涉率尔。而妄意以为此事。元非大段。因此而争端或长。则所伤滋多。不如没之之为愈。故和友之商量也。不以为妨矣。今蒙从容讲订之教。益用愧服。然在拯何敢更容一喙。惟在门下之去取进退之耳。其馀语烦不敢覼缕。且当此阳消之日。不欲更起无益之辨。以犯先人之所深戒者。只佚早晚面承提命而已。
与怀川[五书]
怀川答书曰。日前鄙书其说虽多。不过以为欲破疑惑于胸中。故不避嫌碍云尔。此意如蒙谅察。则彼此都见冰释矣。不然则愚之得罪愈深。而入迷转甚矣。至于阳消之日。更起无益之辨之谕。此诚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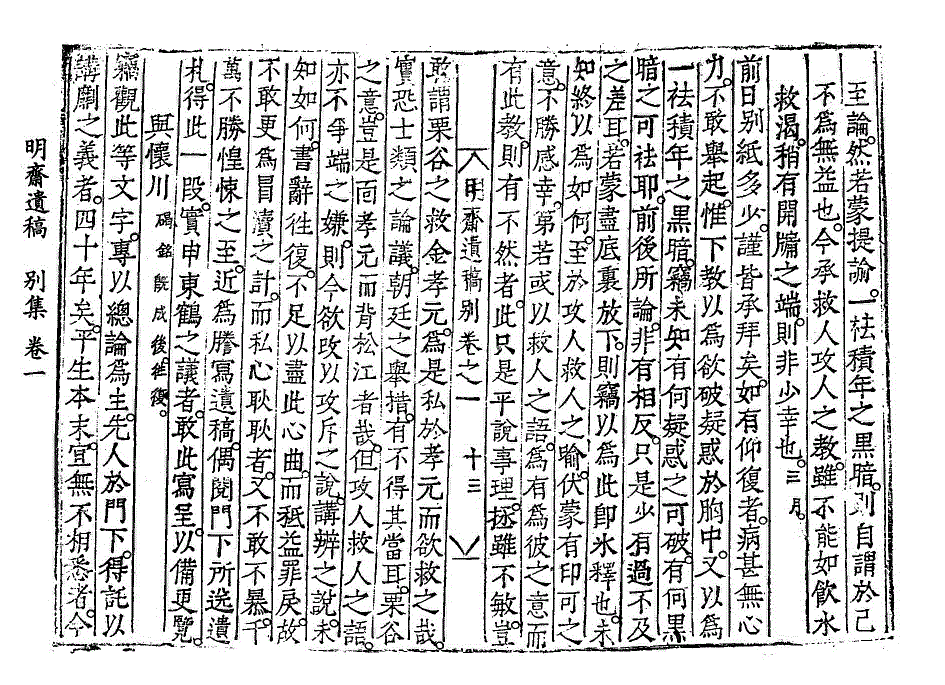 至论。然若蒙提谕。一祛积年之黑暗。则自谓于己不为无益也。今承救人攻人之教。虽不能如饮水救渴。稍有开牖之端。则非少幸也。(三月。)
至论。然若蒙提谕。一祛积年之黑暗。则自谓于己不为无益也。今承救人攻人之教。虽不能如饮水救渴。稍有开牖之端。则非少幸也。(三月。)前日别纸多少。谨皆承拜矣。如有仰复者。病甚无心力。不敢举起。惟下教以为欲破疑惑于胸中。又以为一祛积年之黑暗。窃未知有何疑惑之可破。有何黑暗之可祛耶。前后所论。非有相反。只是少有过不及之差耳。若蒙尽底里放下。则窃以为此即冰释也。未知终以为如何。至于攻人救人之喻。伏蒙有印可之意。不胜感幸。第若或以救人之语。为有为彼之意而有此教。则有不然者。此只是平说事理。拯虽不敏。岂敢谓栗谷之救金孝元。为是私于孝元而欲救之哉。实恐士类之论议。朝廷之举措。有不得其当耳。栗谷之意。岂是面孝元而背松江者哉。但攻人救人之语。亦不争端之嫌。则今欲改以攻斥之说。讲辨之说。未知如何。书辞往复。不足以尽此心曲。而秪益罪戾。故不敢更为冒渎之计。而私心耿耿者。又不敢不暴。千万不胜惶悚之至。近为誊写遗稿。偶阅门下所送遗札。得此一段。实申东鹤之议者。敢此写呈。以备更览。
与怀川(碣铭既成后。往复。)
窃观此等文字。专以总论为主。先人于门下。得托以讲劘之义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无不相悉者。今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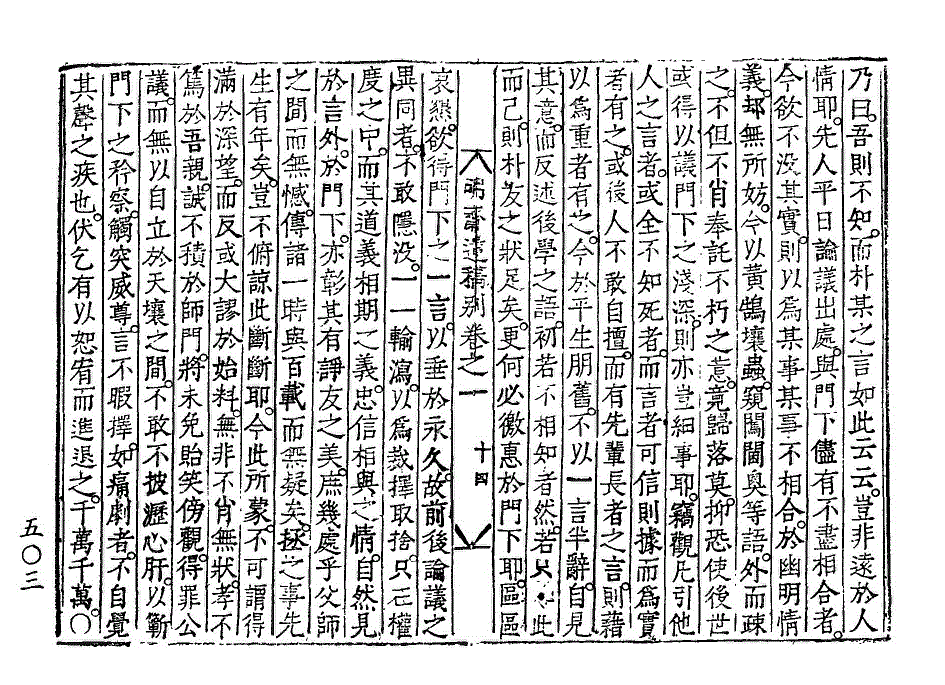 乃曰。吾则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岂非远于人情耶。先人平日论议出处。与门下尽有不尽相合者。今欲不没其实。则以为某事某事不相合。于幽明情义。却无所妨。今以黄鹄壤虫。窥闯阃奥等语。外而疏之。不但不肖奉托不朽之意。竟归落莫。抑恐使后世或得以议门下之浅深。则亦岂细事耶。窃观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则据而为实者有之。或后人不敢自擅。而有先辈长者之言。则藉以为重者有之。今于平生朋旧。不以一言半辞。自见其意。而反述后学之语。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而已。则朴友之状足矣。更何必徼惠于门下耶。区区哀恳。欲得门下之一言。以垂于永久。故前后论议之异同者。不敢隐没。一一输泻。以为裁择取舍。只在权度之中。而其道义相期之义。忠信相与之情。自然见于言外。于门下。亦彰其有诤友之美。庶几处乎父师之间而无憾。传诸一时与百载而无疑矣。拯之事先生有年矣。岂不俯谅此断断耶。今此所蒙。不可谓得满于深望。而反或大谬于始料。无非不肖无状。孝不笃于吾亲。诚不积于师门。将未免贻笑傍观。得罪公议。而无以自立于天壤之间。不敢不披沥心肝。以蕲门下之矜察。触突威尊。言不暇择。如痛剧者。不自觉其声之疾也。伏乞有以恕宥而进退之。千万千万。○
乃曰。吾则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岂非远于人情耶。先人平日论议出处。与门下尽有不尽相合者。今欲不没其实。则以为某事某事不相合。于幽明情义。却无所妨。今以黄鹄壤虫。窥闯阃奥等语。外而疏之。不但不肖奉托不朽之意。竟归落莫。抑恐使后世或得以议门下之浅深。则亦岂细事耶。窃观凡引他人之言者。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则据而为实者有之。或后人不敢自擅。而有先辈长者之言。则藉以为重者有之。今于平生朋旧。不以一言半辞。自见其意。而反述后学之语。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而已。则朴友之状足矣。更何必徼惠于门下耶。区区哀恳。欲得门下之一言。以垂于永久。故前后论议之异同者。不敢隐没。一一输泻。以为裁择取舍。只在权度之中。而其道义相期之义。忠信相与之情。自然见于言外。于门下。亦彰其有诤友之美。庶几处乎父师之间而无憾。传诸一时与百载而无疑矣。拯之事先生有年矣。岂不俯谅此断断耶。今此所蒙。不可谓得满于深望。而反或大谬于始料。无非不肖无状。孝不笃于吾亲。诚不积于师门。将未免贻笑傍观。得罪公议。而无以自立于天壤之间。不敢不披沥心肝。以蕲门下之矜察。触突威尊。言不暇择。如痛剧者。不自觉其声之疾也。伏乞有以恕宥而进退之。千万千万。○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4H 页
 又有一恳。曾见和友出其先铭二本。以为先生先惠一本。而有所禀订。累次往复。则又改惠一本云。其时私窃叹仰其无吝于舍旧而为人之无己也。今此文字总论以下。若蒙改定以赐则固幸。而倘或蒙右例。更出机轴。恐当愈改而愈好矣。妄僭及此。惶恐无地。
又有一恳。曾见和友出其先铭二本。以为先生先惠一本。而有所禀订。累次往复。则又改惠一本云。其时私窃叹仰其无吝于舍旧而为人之无己也。今此文字总论以下。若蒙改定以赐则固幸。而倘或蒙右例。更出机轴。恐当愈改而愈好矣。妄僭及此。惶恐无地。怀川答书曰。忧挠中得奉来书。并两纸之诲。虽不能仔细寻究。大意则可悉矣。盖窃惟念馀人文字。固有忘僭。而妄为题品者矣。至于论道学精深重大者。则见识实有所不逮。不敢容易立说。如李先生后碑。则先辈定论。昭如日星。故只依样胡芦而已。如甑山丈碑文。则状出其哀胤。不可以为引重之资。而今玆状文。实朴和叔极力形容。有他人道不到处。则如愚不肖。何敢攘臂其间。有所删定低昂哉。且愚自视欿然。而尊仰和叔。实如乔岳焉。故意谓此汉借和叔之重。而不甚见陋于后世也。今来书以为后学云。则其与愚见不翅相左矣。且孟子姑舍颜闵。不肯安焉。而及称孔子则反举幸我子贡有若之言。孟子气象。其视三子如何也。况愚之视和叔如右之所陈。则借其重而为说也。不亦宜乎。孟子既举三子之所称。而其自称圣人。则不过仕止久速之当其可而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故今于序文。既以不阿断之至。其铭文。论说中庸之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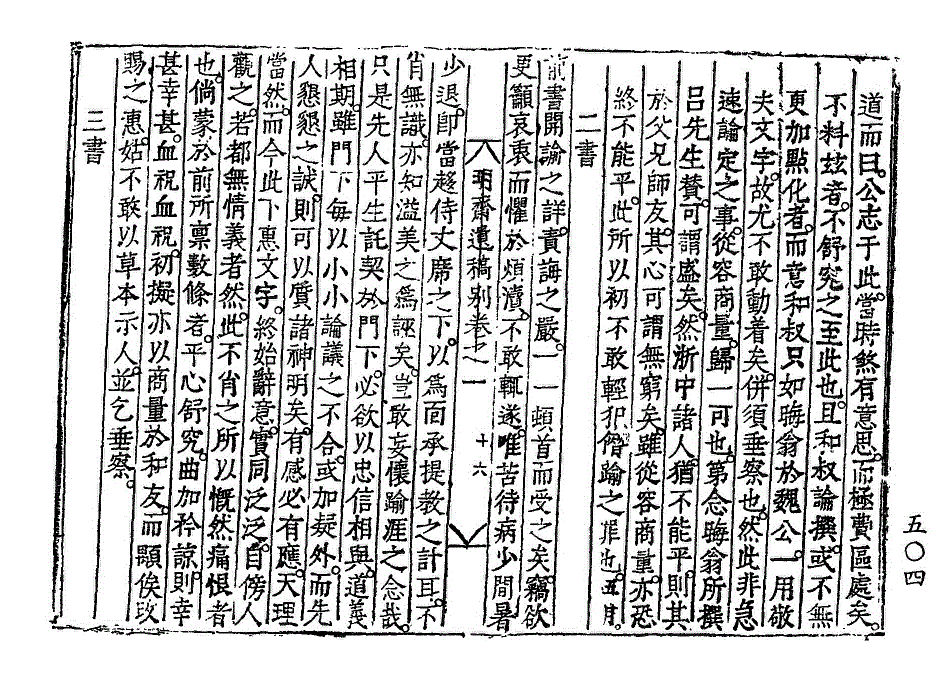 道而曰。公志于此。当时杀有意思。而极费区处矣。不料玆者。不舒究之至此也。且和叔论撰。或不无更加点化者。而意和叔只如晦翁于魏公。一用敬夫文字。故尤不敢动着矣。并须垂察也。然此非急速论定之事。从容商量。归一可也。第念晦翁所撰吕先生赞。可谓盛矣。然浙中诸人。犹不能平。则其于父兄师友。其心可谓无穷矣。虽从容商量。亦恐终不能平。此所以初不敢轻犯僭踰之罪也。(丑月。)
道而曰。公志于此。当时杀有意思。而极费区处矣。不料玆者。不舒究之至此也。且和叔论撰。或不无更加点化者。而意和叔只如晦翁于魏公。一用敬夫文字。故尤不敢动着矣。并须垂察也。然此非急速论定之事。从容商量。归一可也。第念晦翁所撰吕先生赞。可谓盛矣。然浙中诸人。犹不能平。则其于父兄师友。其心可谓无穷矣。虽从容商量。亦恐终不能平。此所以初不敢轻犯僭踰之罪也。(丑月。)与怀川[二书]
前书开谕之详。责诲之严。一一顿首而受之矣。窃欲更吁哀衷而惧于烦渎。不敢辄遂。唯苦待病少间暑少退。即当趋侍丈席之下。以为面承提教之计耳。不肖无识。亦知溢美之为诬矣。岂敢妄怀踰涯之念哉。只是先人平生托契于门下。必欲以忠信相与。道义相期。虽门下每以小小论议之不合。或加疑外。而先人恳恳之诚。则可以质诸神明矣。有感必有应。天理当然。而今此下惠文字。终始辞意。实同泛泛。自傍人观之。若都无情义者然。此不肖之所以慨然痛恨者也。倘蒙于前所禀数条者。平心舒究。曲加矜谅。则幸甚幸甚。血祝血祝。初拟亦以商量于和友。而颙俟改赐之惠。姑不敢以草本示人。并乞垂察。
与怀川[三书]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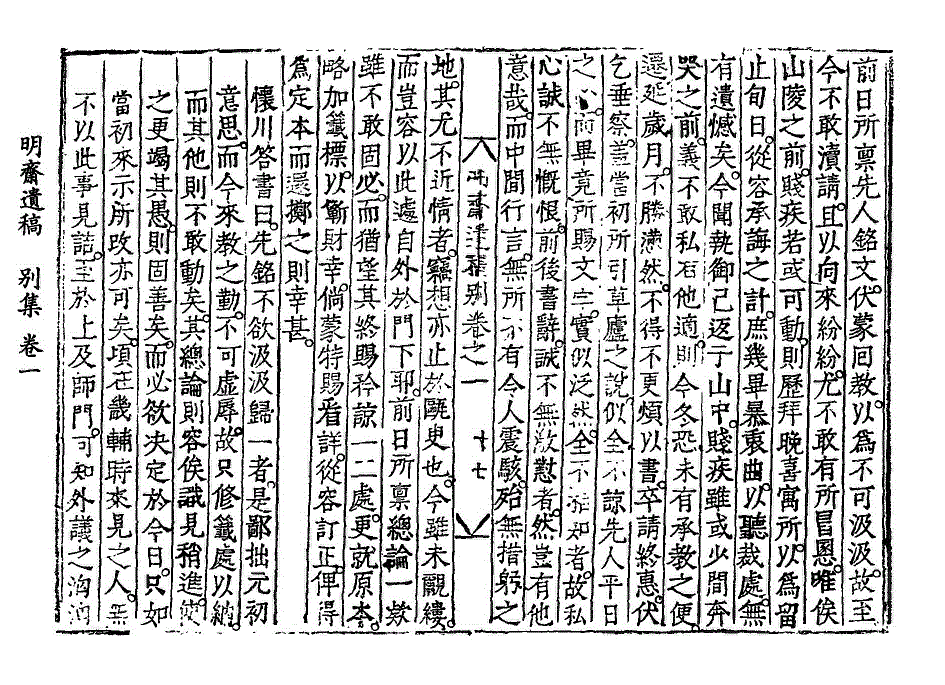 前日所禀先人铭文。伏蒙回教。以为不可汲汲。故至今不敢渎请。且以向来纷纷。尤不敢有所冒慁。唯俟山陵之前。贱疾若或可动。则历拜晚喜寓所。以为留止旬日。从容承诲之计。庶几毕暴衷曲。以听裁处。无有遗憾矣。今闻执御已返于山中。贱疾虽或少间奔哭之前。义不敢私有他适。则今冬恐未有承教之便。迁延岁月。不胜懑然。不得不更烦以书。卒请终惠。伏乞垂察。盖当初所引草庐之说。似全不谅先人平日之心。面毕竟所赐文字。实似泛然。全不相知者。故私心误不无慨恨。前后书辞。诚不无激怼者。然岂有他意哉。而中间行言。无所不有令人震骇。殆无措躬之地。其尤不近情者。窃想亦止于瓯臾也。今虽未覼缕。而岂容以此遽自外于门下耶。前日所禀总论一款虽不敢固必。而犹望其终赐矜谅一二处。更就原本。略加签标。以蕲财幸。倘蒙特赐看详。从容订正。俾得为定本而还掷之则幸甚。
前日所禀先人铭文。伏蒙回教。以为不可汲汲。故至今不敢渎请。且以向来纷纷。尤不敢有所冒慁。唯俟山陵之前。贱疾若或可动。则历拜晚喜寓所。以为留止旬日。从容承诲之计。庶几毕暴衷曲。以听裁处。无有遗憾矣。今闻执御已返于山中。贱疾虽或少间奔哭之前。义不敢私有他适。则今冬恐未有承教之便。迁延岁月。不胜懑然。不得不更烦以书。卒请终惠。伏乞垂察。盖当初所引草庐之说。似全不谅先人平日之心。面毕竟所赐文字。实似泛然。全不相知者。故私心误不无慨恨。前后书辞。诚不无激怼者。然岂有他意哉。而中间行言。无所不有令人震骇。殆无措躬之地。其尤不近情者。窃想亦止于瓯臾也。今虽未覼缕。而岂容以此遽自外于门下耶。前日所禀总论一款虽不敢固必。而犹望其终赐矜谅一二处。更就原本。略加签标。以蕲财幸。倘蒙特赐看详。从容订正。俾得为定本而还掷之则幸甚。怀川答书曰。先铭不欲汲汲归一者。是鄙拙元初意思。而今来教之勤。不可虚辱。故只修签处以纳。而其他则不敢动矣。其总论则容俟识见稍进。使之更竭其愚。则固善矣。而必欲决定于今日。只如当初来示所改亦可矣。顷在畿辅时来见之人。无不以此事见诘。至于上及师门。可知外议之汹汹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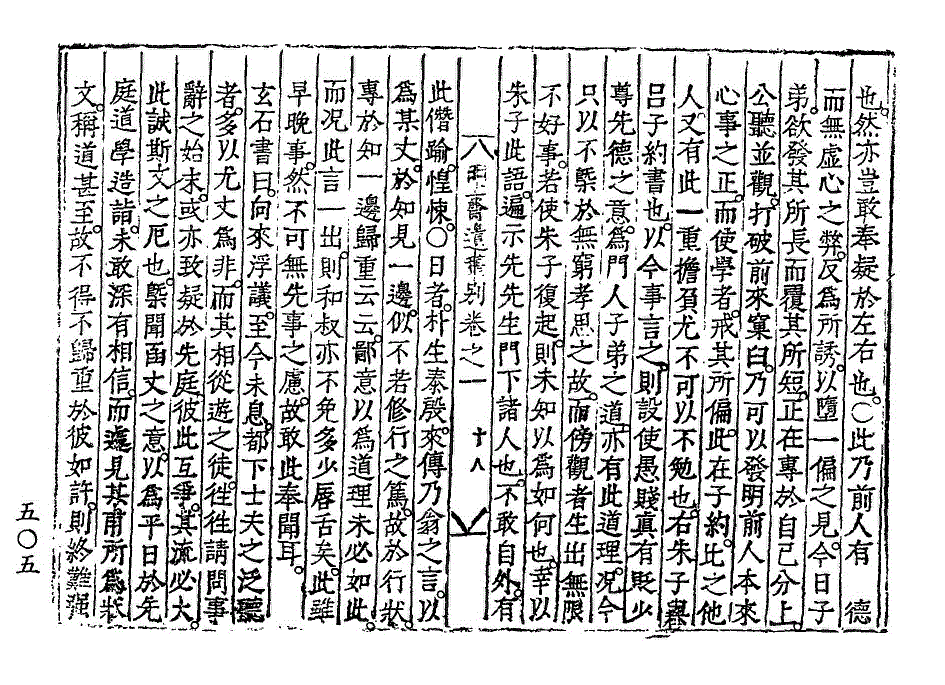 也。然亦岂敢奉疑于左右也。○此乃前人有▣(一作醇)德而无虚心之弊。反为所诱。以堕一偏之见。今日子弟。欲发其所长而覆其所短。正在专于自己分上。公听并观。打破前来窠臼。乃可以发明前人本来心事之正。而使学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约。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担负尤不可以不勉也。右朱子与吕子约书也。以今事言之。则设使愚贱真有贬少尊先德之意。为门人子弟之道。亦有此道理。况今只以不槩于无穷孝思之故。而傍观者生出无限不好事。若使朱子复起。则未知以为如何也。幸以朱子此语。遍示先先生门下诸人也。不敢自外。有此僭踰。惶悚。○日者。朴生泰殷。来传乃翁之言。以为某丈。于知见一边。似不若修行之笃。故于行状。专于知一边归重云云。鄙意以为道理未必如此。而况此言一出。则和叔亦不免多少唇舌矣。此虽早晚事。然不可无先事之虑。故敢此奉闻耳。
也。然亦岂敢奉疑于左右也。○此乃前人有▣(一作醇)德而无虚心之弊。反为所诱。以堕一偏之见。今日子弟。欲发其所长而覆其所短。正在专于自己分上。公听并观。打破前来窠臼。乃可以发明前人本来心事之正。而使学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约。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担负尤不可以不勉也。右朱子与吕子约书也。以今事言之。则设使愚贱真有贬少尊先德之意。为门人子弟之道。亦有此道理。况今只以不槩于无穷孝思之故。而傍观者生出无限不好事。若使朱子复起。则未知以为如何也。幸以朱子此语。遍示先先生门下诸人也。不敢自外。有此僭踰。惶悚。○日者。朴生泰殷。来传乃翁之言。以为某丈。于知见一边。似不若修行之笃。故于行状。专于知一边归重云云。鄙意以为道理未必如此。而况此言一出。则和叔亦不免多少唇舌矣。此虽早晚事。然不可无先事之虑。故敢此奉闻耳。玄石书曰。向来浮议。至今未息。都下士夫之泛听者。多以尤丈为非。而其相从游之徒。往往请问事辞之始末。或亦致疑于先庭彼此互争。其流必大。此诚斯文之厄也。槩闻函丈之意。以为平日于先庭道学造诣。未敢深有相信。而遽见其甫所为状文。称道甚至。故不得不归重于彼如许。则终难强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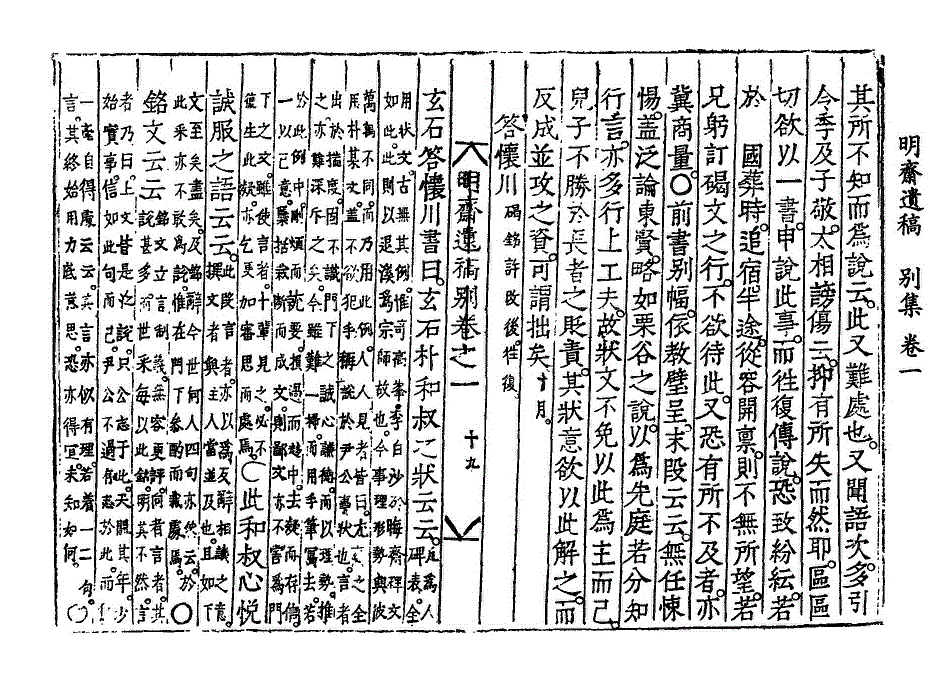 其所不知而为说云。此又难处也。又闻语次。多引令季及子敬。太相谤伤云。抑有所失而然耶。区区切欲以一书。申说此事。而往复传说。恐致纷纭。若于 国葬时。追宿半途。从容开禀。则不无所望。若兄躬订碣文之行。不欲待此。又恐有所不及者。亦冀商量。○前书别幅。依教璧呈。末段云云。无任悚惕。盖泛论东贤。略如栗谷之说。以为先庭若分知行言。亦多行上工夫。故状文不免以此为主而已。儿子不胜于长者之贬责。其状意欲以此解之。而反成并攻之资。可谓拙矣(十月。)
其所不知而为说云。此又难处也。又闻语次。多引令季及子敬。太相谤伤云。抑有所失而然耶。区区切欲以一书。申说此事。而往复传说。恐致纷纭。若于 国葬时。追宿半途。从容开禀。则不无所望。若兄躬订碣文之行。不欲待此。又恐有所不及者。亦冀商量。○前书别幅。依教璧呈。末段云云。无任悚惕。盖泛论东贤。略如栗谷之说。以为先庭若分知行言。亦多行上工夫。故状文不免以此为主而已。儿子不胜于长者之贬责。其状意欲以此解之。而反成并攻之资。可谓拙矣(十月。)答怀川(碣铭许改后。往复)
玄石答怀川书曰。玄石朴和叔之状云云。(凡为人碑表。全用状文。古无其例。惟奇高峰,李白沙于晦斋碑文如此。此则以退溪为宗师故也。今事理形势与彼万万不同。而乃用此例。人人见者皆曰。尤斋之全用朴某文。盖不欲犯手称说于尹公事状也。言者出于揣度。固不诚门下之诚心谦德。而以理势。推之。亦难深斥之矣。今虽难一扫。而用手笔写去。若于此例中。删烦而就要。摈过而趋中。去疑而存信。一以己意。槩括裁断而成文。则鄙文亦不害为门下之文。虽使言者。十辈见之。必不复生此疑。亦乞更加审思而处马。)○此和叔心悦诚服之语云云。(此段言者。亦以为反辞相讥之意。撰文者与主人当并及也。且如下文至矣尽矣。及锦辞今世何人四句亦然云。于世采亦不敢为说。惟在门下参酌而裁处焉。)○铭文云云(铭文立言制议。无容更评。向者言者。其说甚多而世采每以此铭。明其不然。言者乃曰。上文皆是泛说。只公志于此。天阏其年。少始实事。信如此句而已。尹公不过有志于此。而无一毫自得处云云。其言亦似有理。若着一二句。言。其终姶用力底意思。恐亦得宜。未知如何。)○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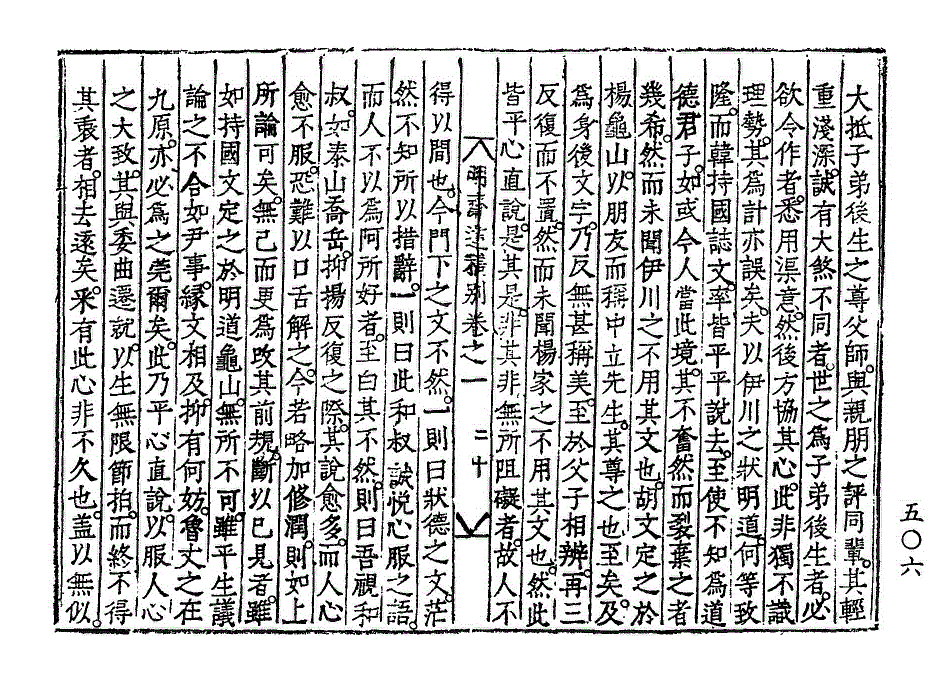 大抵子弟后生之尊父师。与亲朋之评同辈。其轻重浅深。诚有大杀不同者。世之为子弟后生者。必欲令作者。悉用渠意。然后方协其心。此非独不识理势。其为计亦误矣。夫以伊川之状明道。何等致隆。而韩持国志文。率皆平平说去。至使不知为道德君子。如或今人当此境。其不奋然而裂弃之者几希。然而未闻伊川之不用其文也。胡文定之于杨龟山。以朋友而称中立先生。其尊之也至矣。及为身后文字。乃反无甚称美。至于父子相辨。再三反复而不置。然而未闻杨家之不用其文也。然此皆平心直说。是其是。非其非。无所阻碍者。故人不得以间也。今门下之文不然。一则曰状德之文。茫然不知所以措辞。一则曰此和叔诚悦心服之语。而人不以为阿所好者。至白其不然。则曰吾视和叔。如泰山乔岳。抑扬反复之际。其说愈多。而人心愈不服。恐难以口舌解之。今若略加修润。则如上所论可矣。无已而更为改其前规。断以己见者。虽如持国文定之于明道龟山。无所不可。虽平生议论之不合如尹事。缘文相及。抑有何妨。鲁丈之在九原。亦必为之莞尔矣。此乃平心直说。以服人心之大致。其与委曲迁就。以生无限节拍。而终不得其衷者。相去远矣。采有此心非不久也。盖以无似。
大抵子弟后生之尊父师。与亲朋之评同辈。其轻重浅深。诚有大杀不同者。世之为子弟后生者。必欲令作者。悉用渠意。然后方协其心。此非独不识理势。其为计亦误矣。夫以伊川之状明道。何等致隆。而韩持国志文。率皆平平说去。至使不知为道德君子。如或今人当此境。其不奋然而裂弃之者几希。然而未闻伊川之不用其文也。胡文定之于杨龟山。以朋友而称中立先生。其尊之也至矣。及为身后文字。乃反无甚称美。至于父子相辨。再三反复而不置。然而未闻杨家之不用其文也。然此皆平心直说。是其是。非其非。无所阻碍者。故人不得以间也。今门下之文不然。一则曰状德之文。茫然不知所以措辞。一则曰此和叔诚悦心服之语。而人不以为阿所好者。至白其不然。则曰吾视和叔。如泰山乔岳。抑扬反复之际。其说愈多。而人心愈不服。恐难以口舌解之。今若略加修润。则如上所论可矣。无已而更为改其前规。断以己见者。虽如持国文定之于明道龟山。无所不可。虽平生议论之不合如尹事。缘文相及。抑有何妨。鲁丈之在九原。亦必为之莞尔矣。此乃平心直说。以服人心之大致。其与委曲迁就。以生无限节拍。而终不得其衷者。相去远矣。采有此心非不久也。盖以无似。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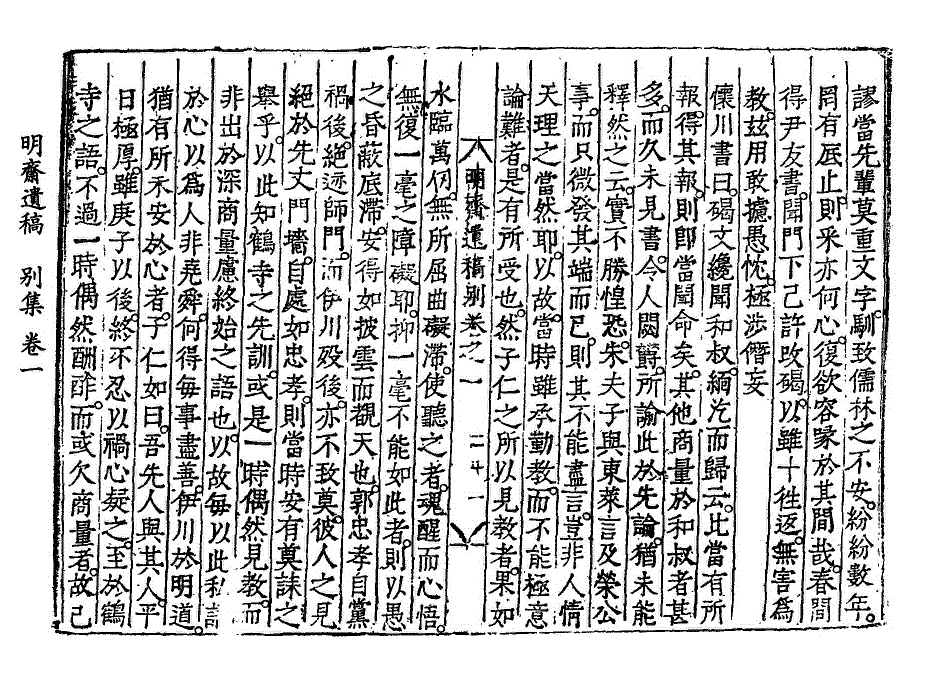 谬当先辈莫重文字。驯致儒林之不安。纷纷数年。罔有底止。则采亦何心。复欲容喙于其间哉。春间得尹友书。闻门下已许改碣。以虽十往返。无害为教。玆用敢摅愚忱。极涉僭妄。
谬当先辈莫重文字。驯致儒林之不安。纷纷数年。罔有底止。则采亦何心。复欲容喙于其间哉。春间得尹友书。闻门下已许改碣。以虽十往返。无害为教。玆用敢摅愚忱。极涉僭妄。怀川书曰。碣文才闻和叔。缅汔而归云。比当有所报。得其报。则即当闻命矣。其他商量于和叔者甚多。而久未见书。令人閟郁。所谕此于先论。犹未能释然之云。实不胜惶恐。朱夫子与东莱言及荣公事。而只微发其端而已。则其不能尽言。岂非人情天理之当然耶。以故。当时虽承勤教。而不能极意论难者。是有所受也。然子仁之所以见教者。果如水临万仞。无所屈曲碍滞。使听之者。魂醒而心悟。无复一毫之障碍耶。抑一毫不能如此者。则以愚之昏蔽底滞。安得如披云而睹天也。郭忠孝自党祸后。绝迹师门。而伊川殁后。亦不致奠。彼人之见绝于先丈门墙。自处如忠孝。则当时安有奠诔之举乎。以此知鹤寺之先训。或是一时偶然见教。而非出于深商量虑终始之语也。以故每以此私语于心以为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伊川于明道。犹有所未安于心者。子仁如曰。吾先人与其人。平日极厚。虽庚子以后。终不忍以祸心疑之。至于鹤寺之语。不过一时偶然酬酢。而或欠商量者。故己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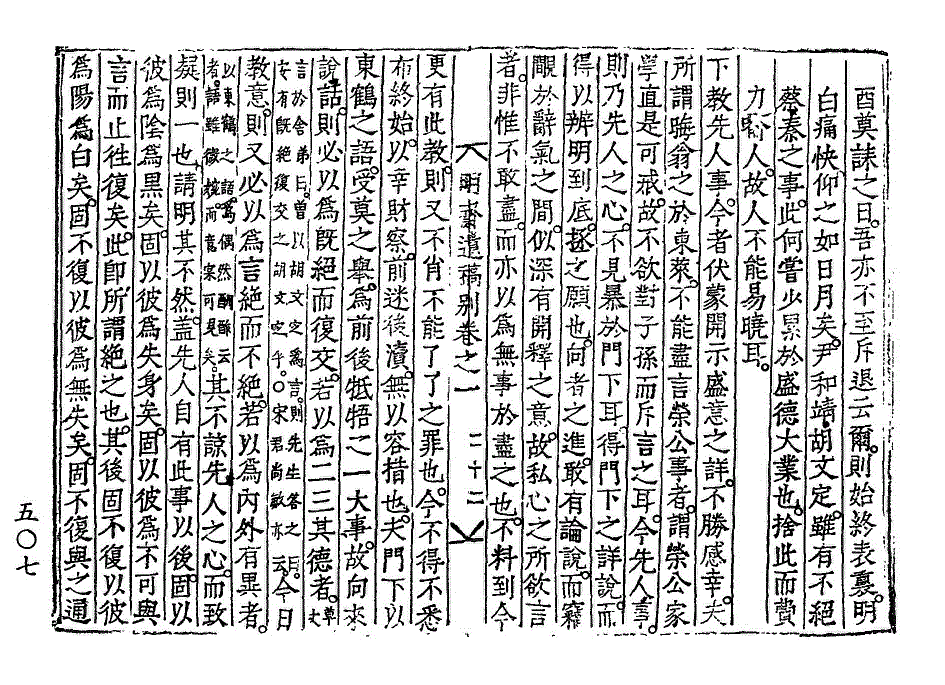 酉奠诔之日。吾亦不至斥退云尔。则始终表里。明白痛快。仰之如日月矣。尹和靖胡文定。虽有不绝蔡秦之事。此何尝少累于盛德大业也。舍此而费力喻人。故人不能易晓耳。
酉奠诔之日。吾亦不至斥退云尔。则始终表里。明白痛快。仰之如日月矣。尹和靖胡文定。虽有不绝蔡秦之事。此何尝少累于盛德大业也。舍此而费力喻人。故人不能易晓耳。下教先人事。今者伏蒙开示盛意之详。不胜感幸。夫所谓晦翁之于东莱。不能尽言荣(一作荥)公事者。谓荣(一作荥)公家学直是可戒。故不欲对子孙而斥言之耳。今先人事。则乃先人之心。不见暴于门下耳。得门下之详说。而得以辨明到底。拯之愿也。向者之进。敢有论说。而窃覵于辞气之间。似深有开释之意。故私心之所欲言者。非惟不敢尽。而亦以为无事于尽之也。不料到今更有此教。则又不肖不能了了之罪也。今不得不悉布终始。以幸财察。前迷后渎。无以容措也。夫门下以东鹤之语。受奠之举。为前后牴牾之一大事。故向来说话。则必以为既绝而复交。若以为二三其德者。(草丈言于舍弟曰。曾以胡文定为言。则先生答之曰。安有既绝复交之胡文定手。○宋君尚敏亦云。)今日教意。则又必以为言绝而不绝。若以为内外有异者。(以来鹤之语。为偶然酬酢云者。语虽微婉。而意实可见矣。)其不谅先人之心。而致疑则一也。请明其不然。盖先人自有此事以后。固以彼为阴为黑矣。固以彼为失身矣。固以彼为不可与言而止往复矣。此即所谓绝之也。其后固不复以彼为阳为白矣。固不复以彼为无失矣。固不复与之通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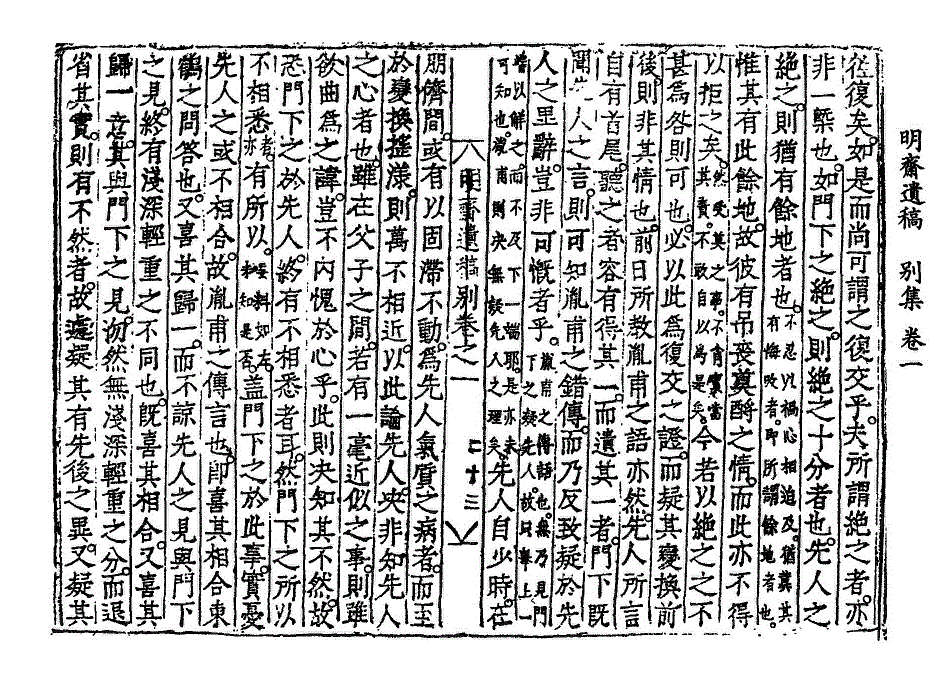 往复矣。如是而尚可谓之复交乎。夫所谓绝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门下之绝之。则绝之十分者也。先人之绝之。则犹有馀地者也。(不忍以祸心相迫及。犹冀其有悔改者。即所谓馀地者也。)惟其有此馀地。故彼有吊丧奠酹之情。而此亦不得以拒之矣。(然受奠之事。不肖实当其责。不敢自以为是矣。)今若以绝之之不甚为咎则可也。必以此为复交之證。而疑其变换前后。则非其情也。前日所教胤甫之语亦然。先人所言自有首尾。听之者容有得其一。而遗其一者。门下既闻先人之言。则可知胤甫之错传。而乃反致疑于先人之异辞。岂非可慨者乎。(胤甫之传话也。无乃见门下之疑先人。故只举上一端以解之。而不及下一媏耶。是亦未可知也。胤甫则决无疑先人之理矣。)先人自少时。在朋侪间。或有以固滞不动。为先人气质之病者。而至于变换摇漾。则万不相近。以此论先人。决非知先人之心者也。虽在父子之间。若有一毫近似之事。则虽欲曲为之讳。岂不内愧于心乎。此则决知其不然。故恐门下之于先人。终有不相悉者耳。然门下之所以不相悉者亦。有所以。(妄料如左。未知是否。)盖门下之于此事。实忧先人之或不相合。故胤甫之传言也。即喜其相合东鹤之问答也。又喜其归一。而不谅先人之见与门下之见。终有浅深轻重之不同也。既喜其相合。又喜其归一意。其与门下之见。沕然无浅深轻重之分。而退省其实。则有不然者。故遽疑其有先后之异。又疑其
往复矣。如是而尚可谓之复交乎。夫所谓绝之者。亦非一槩也。如门下之绝之。则绝之十分者也。先人之绝之。则犹有馀地者也。(不忍以祸心相迫及。犹冀其有悔改者。即所谓馀地者也。)惟其有此馀地。故彼有吊丧奠酹之情。而此亦不得以拒之矣。(然受奠之事。不肖实当其责。不敢自以为是矣。)今若以绝之之不甚为咎则可也。必以此为复交之證。而疑其变换前后。则非其情也。前日所教胤甫之语亦然。先人所言自有首尾。听之者容有得其一。而遗其一者。门下既闻先人之言。则可知胤甫之错传。而乃反致疑于先人之异辞。岂非可慨者乎。(胤甫之传话也。无乃见门下之疑先人。故只举上一端以解之。而不及下一媏耶。是亦未可知也。胤甫则决无疑先人之理矣。)先人自少时。在朋侪间。或有以固滞不动。为先人气质之病者。而至于变换摇漾。则万不相近。以此论先人。决非知先人之心者也。虽在父子之间。若有一毫近似之事。则虽欲曲为之讳。岂不内愧于心乎。此则决知其不然。故恐门下之于先人。终有不相悉者耳。然门下之所以不相悉者亦。有所以。(妄料如左。未知是否。)盖门下之于此事。实忧先人之或不相合。故胤甫之传言也。即喜其相合东鹤之问答也。又喜其归一。而不谅先人之见与门下之见。终有浅深轻重之不同也。既喜其相合。又喜其归一意。其与门下之见。沕然无浅深轻重之分。而退省其实。则有不然者。故遽疑其有先后之异。又疑其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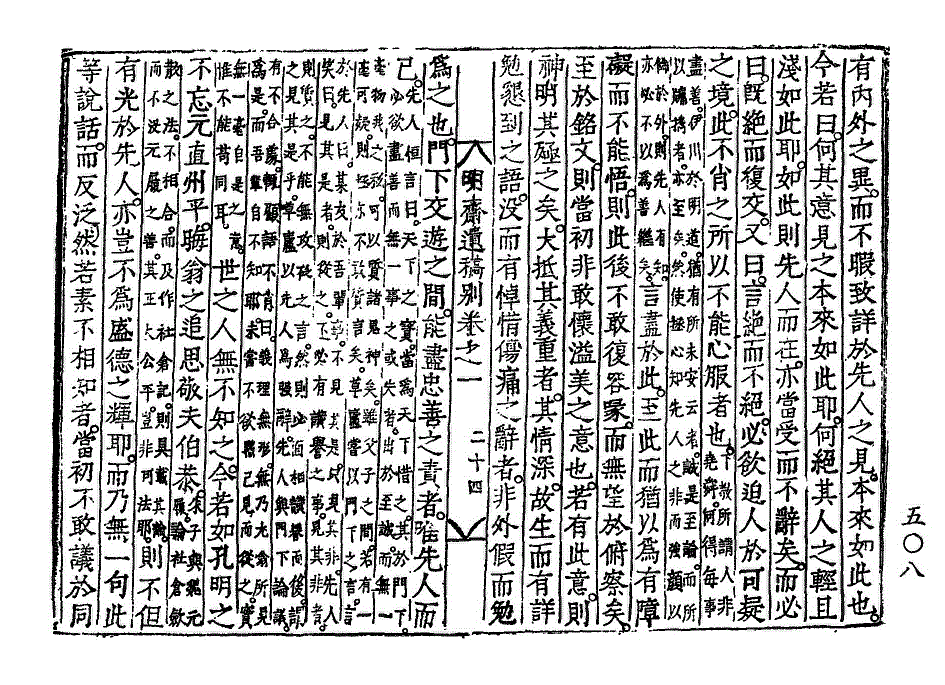 有内外之异。而不暇致详于先人之见。本来如此也。今若曰。何其意见之本来如此耶。何绝其人之轻且浅如此耶。如此则先人而在。亦当受而不辞矣。而必曰。既绝而复交。又曰。言绝而不绝。必欲迫人于可疑之境。此不肖之所以不能心服者也。(下教所谓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伊川于明道。犹有所未安云者。诚是至论。而所以牖携者。亦至矣。然使拯心知先人之非而强颜以饰于外。则先人有知。亦必不以为善继矣。)言尽于此。至此而犹以为有障碍而不能悟。则此后不敢复容喙。而无望于俯察矣。至于铭文。则当初非敢怀溢美之意也。若有此意。则神明其殛之矣。大抵其义重者。其情深。故生而有详勉恳到之语。没而有悼惜伤痛之辞者。非外假而勉为之也。门下交游之间。能尽忠善之责者。唯先人而已。(先人恒言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其于门下。必欲尽善而无一事之或失者。出于至诚。而无一毫物我之私。可以质诸鬼神矣。虽父子之间。若有一毫可疑。则拯亦不敢质言矣。草庐尝以门下之言。言于先人曰。某友于吾辈事。不见其是。只见其非。先人笑曰。见其是者。则从之。丕必有赞誉之事。见其非者。则质之。不能无攻砭之言。然则必面相赞誉而后。谓之见其是乎。草庐以先人为强辞。先人与门下论议。有不合处。辄顾语不肖曰。义理无形。无乃尤翁所见为是。而吾辈自不知耶。未尝不欲黜己见而从之。实无一毫自是之意。惟不能苟同耳。)世之人无不知之。今若如孔明之不忘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朱子与魏元履。论社仓敛散之法。不相合。而及作社仓记。则具载其论。而不没元履之善。其正大公平。岂非可法耶。)则不但有光于先人。亦岂不为盛德之辉耶。而乃无一句此等说话。而反泛然若素不相知者。当初不敢议于同
有内外之异。而不暇致详于先人之见。本来如此也。今若曰。何其意见之本来如此耶。何绝其人之轻且浅如此耶。如此则先人而在。亦当受而不辞矣。而必曰。既绝而复交。又曰。言绝而不绝。必欲迫人于可疑之境。此不肖之所以不能心服者也。(下教所谓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伊川于明道。犹有所未安云者。诚是至论。而所以牖携者。亦至矣。然使拯心知先人之非而强颜以饰于外。则先人有知。亦必不以为善继矣。)言尽于此。至此而犹以为有障碍而不能悟。则此后不敢复容喙。而无望于俯察矣。至于铭文。则当初非敢怀溢美之意也。若有此意。则神明其殛之矣。大抵其义重者。其情深。故生而有详勉恳到之语。没而有悼惜伤痛之辞者。非外假而勉为之也。门下交游之间。能尽忠善之责者。唯先人而已。(先人恒言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其于门下。必欲尽善而无一事之或失者。出于至诚。而无一毫物我之私。可以质诸鬼神矣。虽父子之间。若有一毫可疑。则拯亦不敢质言矣。草庐尝以门下之言。言于先人曰。某友于吾辈事。不见其是。只见其非。先人笑曰。见其是者。则从之。丕必有赞誉之事。见其非者。则质之。不能无攻砭之言。然则必面相赞誉而后。谓之见其是乎。草庐以先人为强辞。先人与门下论议。有不合处。辄顾语不肖曰。义理无形。无乃尤翁所见为是。而吾辈自不知耶。未尝不欲黜己见而从之。实无一毫自是之意。惟不能苟同耳。)世之人无不知之。今若如孔明之不忘元直州平。晦翁之追思敬夫伯恭。(朱子与魏元履。论社仓敛散之法。不相合。而及作社仓记。则具载其论。而不没元履之善。其正大公平。岂非可法耶。)则不但有光于先人。亦岂不为盛德之辉耶。而乃无一句此等说话。而反泛然若素不相知者。当初不敢议于同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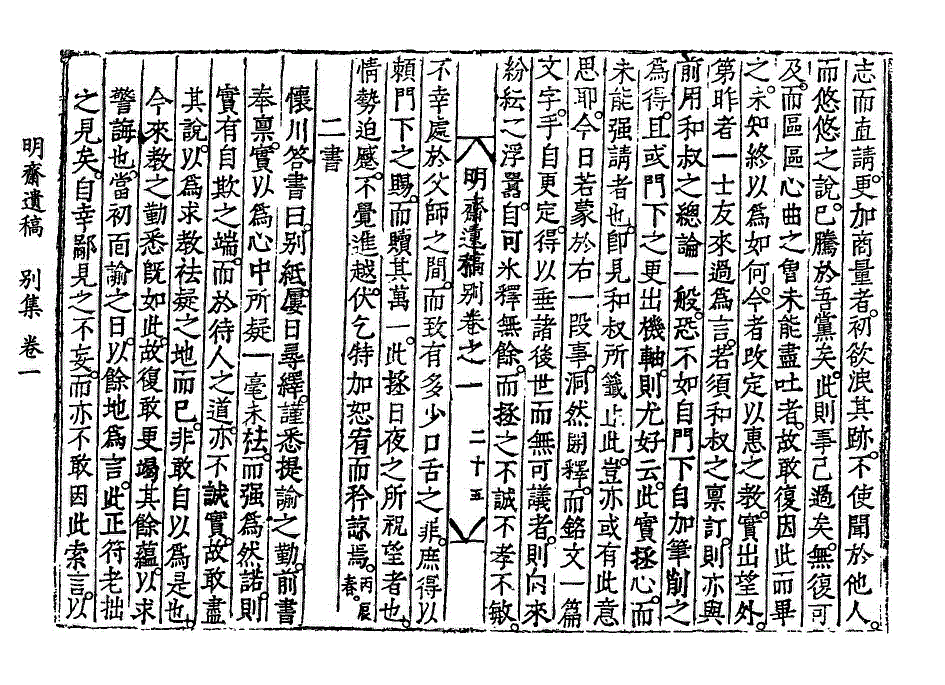 志而直请。更加商量者。初欲泯其迹。不使闻于他人。而悠悠之说。已腾于吾党矣。此则事已过矣。无复可及。而区区心曲之曾未能尽吐者。故敢复因此而毕之。未知终以为如何。今者改定以惠之教。实出望外。第昨者一士友来过为言。若须和叔之禀订。则亦与前用和叔之总论一般。恐不如自门下自加笔削之为得。且或门下之更出机轴。则尤好云。此实拯心。而未能强请者也。即见和叔所签止此。岂亦或有此意思耶。今日若蒙于右一段事。洞然开释。而铭文一篇文字。手自更定。得以垂诸后世而无可议者。则向来纷纭之浮嚣。自可冰释无馀。而拯之不诚不孝不敏。不幸处于父师之间。而致有多少口舌之非。庶得以赖门下之赐。而赎其万一。此拯日夜之所祝望者也。情势迫蹙。不觉进越。伏乞特加恕宥而矜谅焉。(丙辰春。)
志而直请。更加商量者。初欲泯其迹。不使闻于他人。而悠悠之说。已腾于吾党矣。此则事已过矣。无复可及。而区区心曲之曾未能尽吐者。故敢复因此而毕之。未知终以为如何。今者改定以惠之教。实出望外。第昨者一士友来过为言。若须和叔之禀订。则亦与前用和叔之总论一般。恐不如自门下自加笔削之为得。且或门下之更出机轴。则尤好云。此实拯心。而未能强请者也。即见和叔所签止此。岂亦或有此意思耶。今日若蒙于右一段事。洞然开释。而铭文一篇文字。手自更定。得以垂诸后世而无可议者。则向来纷纭之浮嚣。自可冰释无馀。而拯之不诚不孝不敏。不幸处于父师之间。而致有多少口舌之非。庶得以赖门下之赐。而赎其万一。此拯日夜之所祝望者也。情势迫蹙。不觉进越。伏乞特加恕宥而矜谅焉。(丙辰春。)答怀川[二书]
怀川答书曰。别纸屡日寻绎。谨悉提谕之勤。前书奉禀。实以为心中所疑一毫未祛。而强为然诺。则实有自欺之端。而于待人之道。亦不诚实。故敢尽其说。以为求教祛疑之地而已。非敢自以为是也。今来教之勤悉既如此。故复敢更竭其馀蕴。以求警诲也。当初面谕之日。以馀地为言。此正符老拙之见矣。自幸鄙见之不妄。而亦不敢因此索言。以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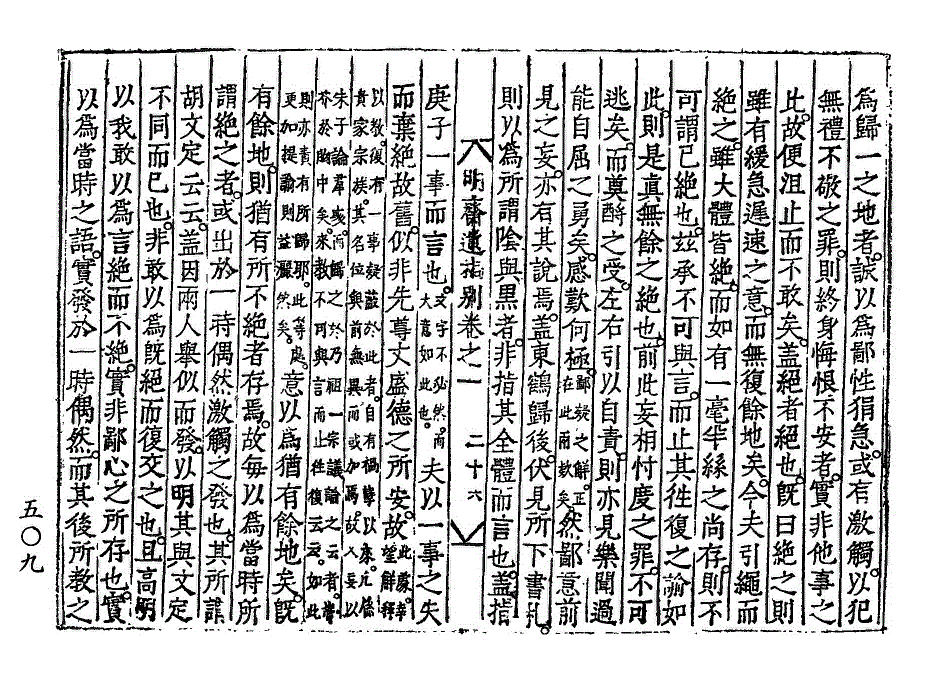 为归一之地者。诚以为鄙性狷急。或有激触。以犯无礼不敬之罪。则终身悔恨不安者。实非他事之比。故便沮止而不敢矣。盖绝者绝也。既曰绝之则虽有缓急迟速之意。而无复馀地矣。今夫引绳而绝之。虽大体皆绝。而如有一毫半丝之尚存。则不可谓已绝也。玆承不可与言。而止其往复之谕如此。则是真无馀之绝也。前此妄相忖度之罪。不可逃矣。而奠酹之受。左右引以自责。则亦见乐闻过能自屈之勇矣。感叹何极。(鄙疑之解。正在此两款矣。)然鄙意前见之妄。亦有其说焉。盖东鹤归后。伏见所下书札。则以为所谓阴与黑者。非指其全体而言也。盖指庚子一事而言也。(文字不必然。而大意如此也。)夫以一事之失而弃绝故旧。似非先尊文盛德之所安。故(此处。幸望解释以教。复有一事疑蔽于此者。自有祸孽以来。凡信贵家宗族。其名位与前无异而或加焉。故人妄以朱子论群彧。而归之于乃祖一宗议论之云者。▦芥于胸中矣。来教不可与言而止往复云云。如此则亦责有所归耶。此等处。更加提谕则益洒然矣。)意以为犹有馀地矣。既有馀地。则犹有所不绝者存焉。故每以为当时所谓绝之者。或出于一时偶然激触之发也。其所谓胡文定云云。盖因两人举似而发。以明其与文定不同而已也。非敢以为既绝而复交之也。且高明以我敢以为言绝而不绝。实非鄙心之所存也。实以为当时之语。实发于一时偶然。而其后所教之
为归一之地者。诚以为鄙性狷急。或有激触。以犯无礼不敬之罪。则终身悔恨不安者。实非他事之比。故便沮止而不敢矣。盖绝者绝也。既曰绝之则虽有缓急迟速之意。而无复馀地矣。今夫引绳而绝之。虽大体皆绝。而如有一毫半丝之尚存。则不可谓已绝也。玆承不可与言。而止其往复之谕如此。则是真无馀之绝也。前此妄相忖度之罪。不可逃矣。而奠酹之受。左右引以自责。则亦见乐闻过能自屈之勇矣。感叹何极。(鄙疑之解。正在此两款矣。)然鄙意前见之妄。亦有其说焉。盖东鹤归后。伏见所下书札。则以为所谓阴与黑者。非指其全体而言也。盖指庚子一事而言也。(文字不必然。而大意如此也。)夫以一事之失而弃绝故旧。似非先尊文盛德之所安。故(此处。幸望解释以教。复有一事疑蔽于此者。自有祸孽以来。凡信贵家宗族。其名位与前无异而或加焉。故人妄以朱子论群彧。而归之于乃祖一宗议论之云者。▦芥于胸中矣。来教不可与言而止往复云云。如此则亦责有所归耶。此等处。更加提谕则益洒然矣。)意以为犹有馀地矣。既有馀地。则犹有所不绝者存焉。故每以为当时所谓绝之者。或出于一时偶然激触之发也。其所谓胡文定云云。盖因两人举似而发。以明其与文定不同而已也。非敢以为既绝而复交之也。且高明以我敢以为言绝而不绝。实非鄙心之所存也。实以为当时之语。实发于一时偶然。而其后所教之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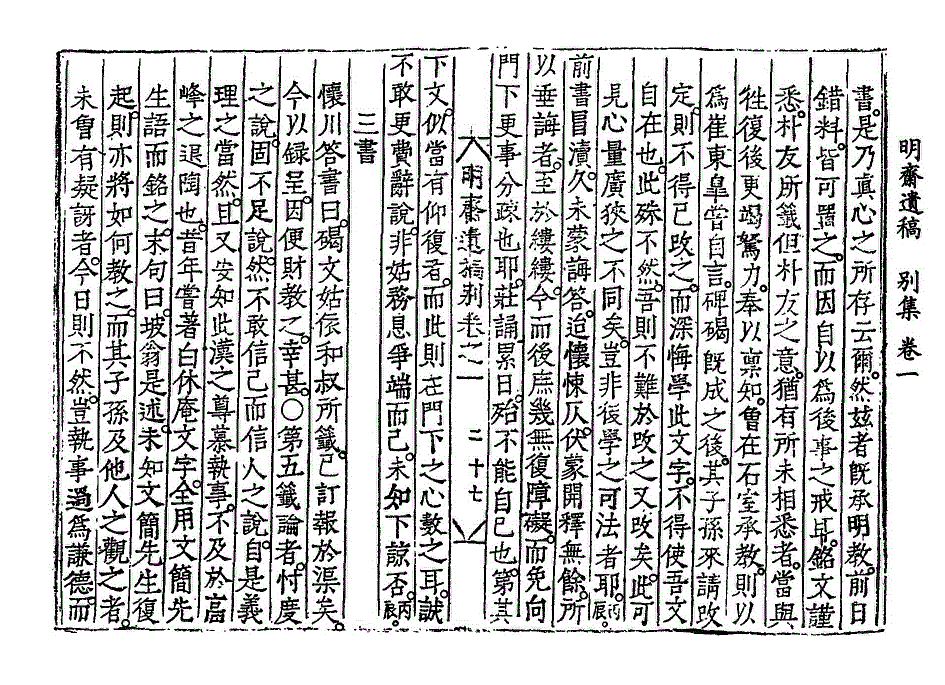 书。是乃真心之所存云尔。然玆者既承明教。前日错料。皆可置之。而因自以为后事之戒耳。铭文谨悉。朴友所签。但朴友之意。犹有所未相悉者。当与往复后更竭驽力。奉以禀知。曾在石室承教。则以为崔东皋尝自言。碑碣既成之后。其子孙来请改定。则不得已改之。而深悔学此文字。不得使吾文自在也。此殊不然。吾则不难于改之又改矣。此可见心量广狭之不同矣。岂非后学之可法者耶。(丙辰。)
书。是乃真心之所存云尔。然玆者既承明教。前日错料。皆可置之。而因自以为后事之戒耳。铭文谨悉。朴友所签。但朴友之意。犹有所未相悉者。当与往复后更竭驽力。奉以禀知。曾在石室承教。则以为崔东皋尝自言。碑碣既成之后。其子孙来请改定。则不得已改之。而深悔学此文字。不得使吾文自在也。此殊不然。吾则不难于改之又改矣。此可见心量广狭之不同矣。岂非后学之可法者耶。(丙辰。)前书冒渎。久未蒙诲答。迨怀悚仄。伏蒙开释无馀。所以垂诲者。至于缕缕。今而后庶几无复障凝。而免向门下更事分疏也耶。庄诵累日。殆不能自已也。第其下文。似当有仰复者。而此则在门下之心数之耳。诚不敢更费辞说。非姑务息争端而已。未知下谅否。(丙辰。)
答怀川[三书]
怀川答书曰。碣文姑依和叔所签。已订报于渠矣。今以录呈。因便财教之。幸甚。○第五签论者。忖度之说。固不足说。然不敢信己而信人之说。自是义理之当然。且又安知此汉之尊慕执事。不及于高峰之退陶也。昔年尝著白休庵文字。全用文简先生语而铭之。末句曰。坡翁是述。未知文简先生复起。则亦将如何教之。而其子孙及他人之观之者。未曾有疑讶者。今日则不然。岂执事过为谦德。而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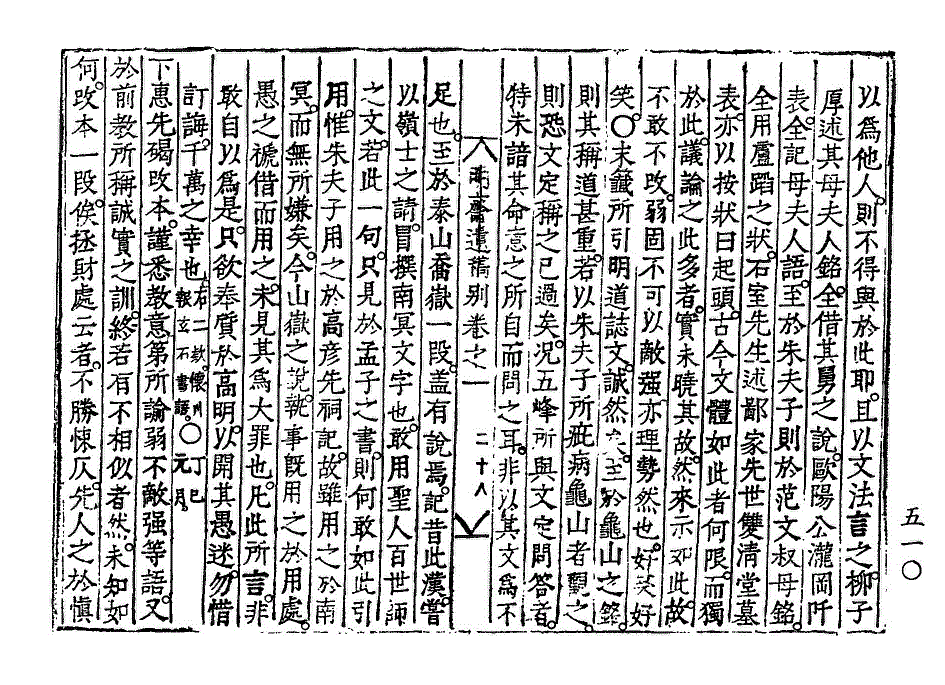 以为他人。则不得与于此耶。且以文法言之。柳子厚述其母夫人铭。全借其舅之说。欧阳公泷冈阡表。全记母夫人语。至于朱夫子则于范文叔母铭。全用卢蹈之状。石室先生述鄙家先世双清堂墓表。亦以按状曰起头。古今文体如此者何限。而独于此。议论之此多者。实未晓其故。然来示如此。故不敢不改。弱固不可以敌强。亦理势然也。好笑好笑。○末签所引明道志文。诚然矣。至于龟山之铭。则其称道甚重。若以朱夫子所疵病龟山者观之。则恐文定称之已过矣。况五峰所与文定问答者。特未谙其命意之所自而问之耳。非以其文为不足也。至于泰山乔岳一段。盖有说焉。记昔此汉。尝以岭士之请。冒撰南冥文字也。敢用圣人百世师之文。若此一句。只见于孟子之书。则何敢如此引用。惟朱夫子用之于高彦先祠记。故虽用之于南冥。而无所嫌矣。今山岳之说。执事既用之于用处。愚之褫借而用之。未见其为大罪也。凡此所言。非敢自以为是。只欲奉质于高明。以开其愚迷。勿惜订诲。千万之幸也。(右二款。怀川报玄石书语。)○(丁巳元月。)
以为他人。则不得与于此耶。且以文法言之。柳子厚述其母夫人铭。全借其舅之说。欧阳公泷冈阡表。全记母夫人语。至于朱夫子则于范文叔母铭。全用卢蹈之状。石室先生述鄙家先世双清堂墓表。亦以按状曰起头。古今文体如此者何限。而独于此。议论之此多者。实未晓其故。然来示如此。故不敢不改。弱固不可以敌强。亦理势然也。好笑好笑。○末签所引明道志文。诚然矣。至于龟山之铭。则其称道甚重。若以朱夫子所疵病龟山者观之。则恐文定称之已过矣。况五峰所与文定问答者。特未谙其命意之所自而问之耳。非以其文为不足也。至于泰山乔岳一段。盖有说焉。记昔此汉。尝以岭士之请。冒撰南冥文字也。敢用圣人百世师之文。若此一句。只见于孟子之书。则何敢如此引用。惟朱夫子用之于高彦先祠记。故虽用之于南冥。而无所嫌矣。今山岳之说。执事既用之于用处。愚之褫借而用之。未见其为大罪也。凡此所言。非敢自以为是。只欲奉质于高明。以开其愚迷。勿惜订诲。千万之幸也。(右二款。怀川报玄石书语。)○(丁巳元月。)下惠先碣改本。谨悉教意。第所谕弱不敌强等语。又于前教所称诚实之训。终若有不相似者然。未知如何。改本一段。俟拯财处云者。不胜悚仄。先人之于慎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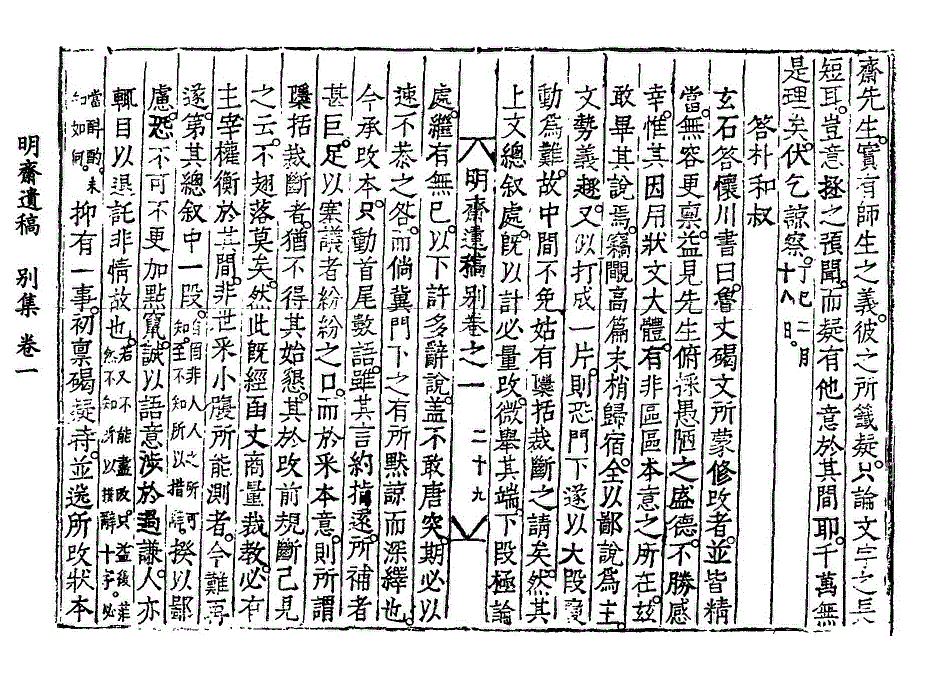 斋先生。实有师生之义。彼之所签疑。只论文字之长短耳。岂意拯之预闻。而疑有他意于其间耶。千万无是理矣。伏乞谅察。(丁巳二月十八日。)
斋先生。实有师生之义。彼之所签疑。只论文字之长短耳。岂意拯之预闻。而疑有他意于其间耶。千万无是理矣。伏乞谅察。(丁巳二月十八日。)答朴和叔
玄石答怀川书曰。鲁丈碣文所蒙修改者。并皆精当。无容更禀。益见先生俯采愚陋之盛德。不胜感幸。惟其因用状文大体。有非区区本意之所在。玆敢毕其说焉。窃覵高篇末梢归宿。全以鄙说为主。文势义趣。又以打成一片。则恐门下遂以大段变动为难。故中间不免姑有檃括裁断之请矣。然其上文总叙处。既以计必量改。微举其端下段极论处。继有无已。以下许多辞说。盖不敢唐突。期必以速不恭之咎。而倘冀门下之有所默谅而深绎也。今承改本。只动首尾数语。虽其言约指远。所补者甚巨。足以塞议者纷纷之口。而于采本意。则所谓檃括裁断者。犹不得其始恳。其于改前规断已见之云。不翅落莫矣。然此既经函丈商量裁教。必有主宰权衡于其间。非世采小腹所能测者。今难再遂。第其总叙中一段。(自固非人人之所可知。至不知所以措辞)揆以鄙虑。恐不可不更加点窜。诚以语意涉于过谦。人亦辄目以退托非情故也。(若又不能尽改。只益复庄然不知所以辞十字。必当斟酌。未知如何。)抑有一事。初禀碣疑待。并送所改状本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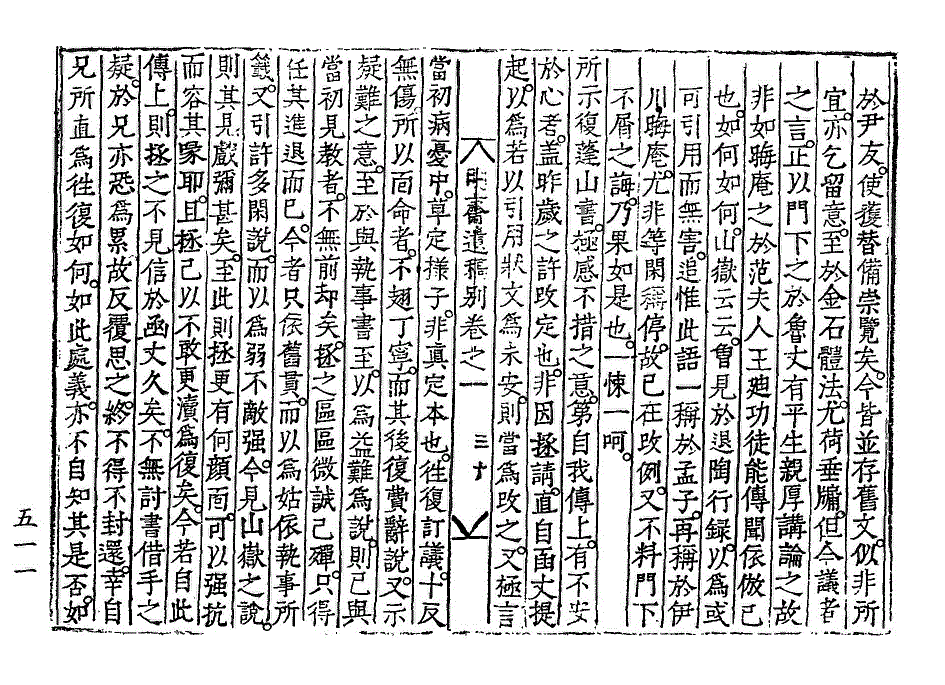 于尹友。使获替备崇览矣。今皆并存旧文。似非所宜。亦乞留意。至于金石体法。尤荷垂牖。但今议者之言。正以门下之于鲁丈有平生亲厚讲论之故非如晦庵之于范夫人王迪功徒能传闻依仿已也。如何如何。山岳云云。曾见于退陶行录。以为或可引用而无害。追惟此语一称于孟子。再称于伊川,晦庵。尤非等闲称停。故已在改例。又不料门下不屑之诲。乃果如是也。一悚一呵。
于尹友。使获替备崇览矣。今皆并存旧文。似非所宜。亦乞留意。至于金石体法。尤荷垂牖。但今议者之言。正以门下之于鲁丈有平生亲厚讲论之故非如晦庵之于范夫人王迪功徒能传闻依仿已也。如何如何。山岳云云。曾见于退陶行录。以为或可引用而无害。追惟此语一称于孟子。再称于伊川,晦庵。尤非等闲称停。故已在改例。又不料门下不屑之诲。乃果如是也。一悚一呵。所示复蓬山书。极感不措之意。第自我传上。有不安于心者。盖昨岁之许改定也。非因拯请。直自函丈提起。以为若以引用状文为未安。则当为改之。又极言当初病忧中。草定样子。非真定本也。往复订议。十反无伤。所以面命者。不翅丁宁。而其后复费辞说。又示疑难之意。至于与执事书至。以为益难为说。则已与当初见教者。不无前却矣。拯之区区微诚已殚。只得任其进退而已。今者只依旧贯。而以为姑依执事所签。又引许多闲说。而以为弱不敌强。今见山岳之说。则其见献弥甚矣。至此则拯更有何颜面。可以强抗而容其喙耶。且拯已以不敢更渎为复矣。今若自此传上。则拯之不见信于函丈久矣。不无讨书借手之疑。于兄亦恐为累。故反覆思之。终不得不封还。幸自兄所直为往复如何。如此处义。亦不自知其是否。如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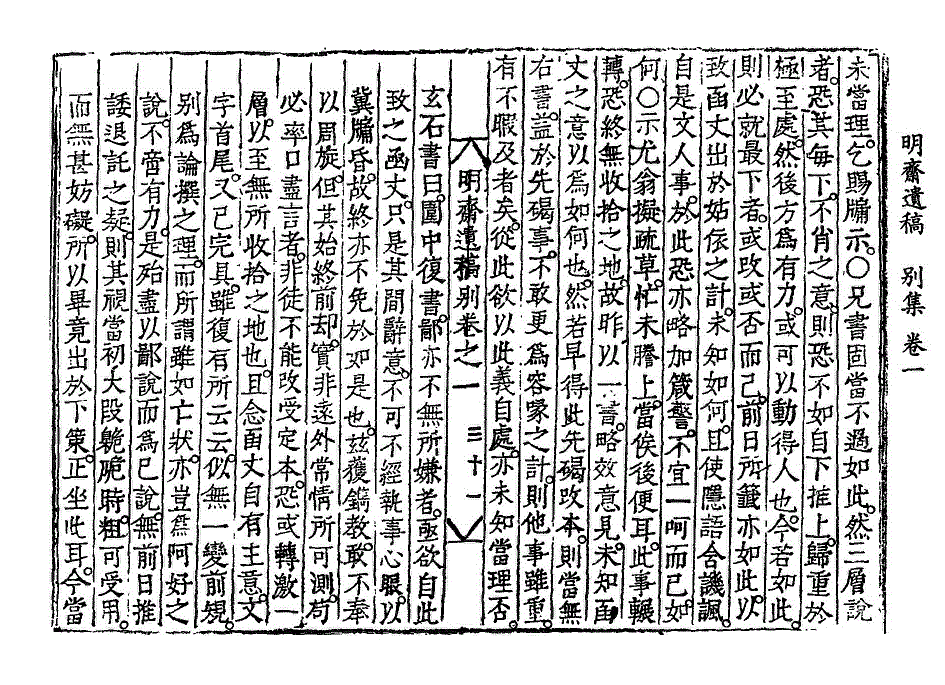 未当理。乞赐牖示。○兄书固当不过如此。然三层说者。恐其每下。不肖之意。则恐不如自下推上。归重于极至处。然后方为有力。或可以动得人也。今若如此。则必就最下者。或改或否而已。前日所签亦如此。以致函丈出于姑依之计。未知如何。且使隐语含讥讽。自是文人事。于此恐亦略加箴警。不宜一呵而已。如何○示尤翁拟疏草。忙未誊上。当俟后便耳。此事辗转。恐终无收拾之地。故昨以一书。略效意见。未知函丈之意以为如何也。然若早得此先碣改本。则当无右书。盖于先碣事。不敢更为容喙之计。则他事虽重。有不暇及者矣。从此欲以此义自处。亦未知当理否。
未当理。乞赐牖示。○兄书固当不过如此。然三层说者。恐其每下。不肖之意。则恐不如自下推上。归重于极至处。然后方为有力。或可以动得人也。今若如此。则必就最下者。或改或否而已。前日所签亦如此。以致函丈出于姑依之计。未知如何。且使隐语含讥讽。自是文人事。于此恐亦略加箴警。不宜一呵而已。如何○示尤翁拟疏草。忙未誊上。当俟后便耳。此事辗转。恐终无收拾之地。故昨以一书。略效意见。未知函丈之意以为如何也。然若早得此先碣改本。则当无右书。盖于先碣事。不敢更为容喙之计。则他事虽重。有不暇及者矣。从此欲以此义自处。亦未知当理否。玄石书曰。围中复书。鄙亦不无所嫌者。亟欲自此致之函丈。只是其间辞意。不可不经执事心眼。以冀牖昏。故终亦不免于如是也。玆获镌教。敢不奉以周旋。但其始终前却。实非远外常情所可测。苟必率口尽言者。非徒不能改受定本。恐或转激一层。以至无所收拾之地也。且念函丈自有主意。文字首尾。又已完具。虽复有所云云。似无一变前规。别为论撰之理。而所谓虽如亡状。亦岂为阿好之说。不啻有力。是殆尽以鄙说而为己说。无前日推诿退托之疑。则其视当初大段臲卼时。粗可受用。而无甚妨碍。所以毕竟出于下策。正坐此耳。今当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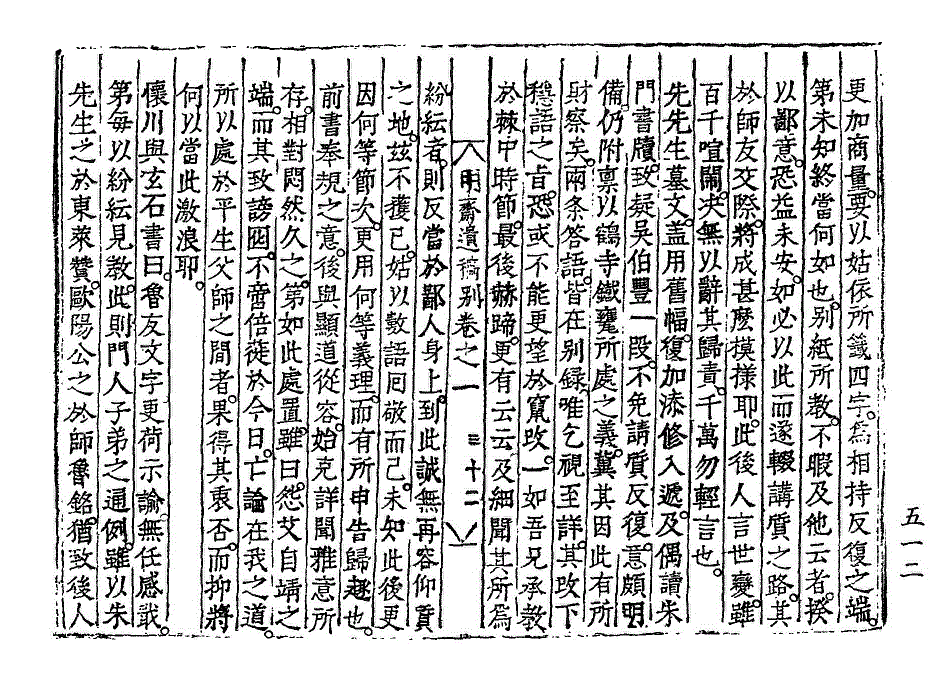 更加商量。要以姑依所签四字。为相持反复之端。第未知终当何如也。别纸所教。不暇及他云者。揆以鄙意。恐益未安。如必以此而遂辍讲质之路。其于师友交际。将成甚么模样耶。此后人言世变。虽百千喧闹。决无以辞其归责。千万勿轻言也。
更加商量。要以姑依所签四字。为相持反复之端。第未知终当何如也。别纸所教。不暇及他云者。揆以鄙意。恐益未安。如必以此而遂辍讲质之路。其于师友交际。将成甚么模样耶。此后人言世变。虽百千喧闹。决无以辞其归责。千万勿轻言也。先先生墓文。盖用旧幅。复加漆修入递。及偶读朱门书牍。致疑吴伯丰一段。不免请质反复。意颇明备。仍附禀以鹤寺铁瓮所处之义。冀其因此有所财察矣。两条答语。皆在别录。唯乞视至详。其改下稳语之旨。恐或不能更望于窜改。一如吾兄承教于棘中时节。最后赫蹄。更有云云。及细闻其所为纷纭者。则反当于鄙人身上。到此诚无再容仰质之地。玆不获已。姑以数语回敬而已。未知此后更因何等节次。更用何等义理。而有所申告归趣也。前书奉规之意。后与显道从容。始克详闻雅意所存。相对闷然久之。第如此处置。虽曰。怨艾自靖之端。而其致谤囮。不啻倍蓰于今日。亡论在我之道。所以处于平生父师之间者。果得其衷否。而抑将何以当此激浪耶。
怀川与玄石书曰。鲁友文字更荷示谕。无任感戢。第每以纷纭见教。此则门人子弟之通例。虽以朱先生之于东莱赞。欧阳公之于师鲁铭。犹致后人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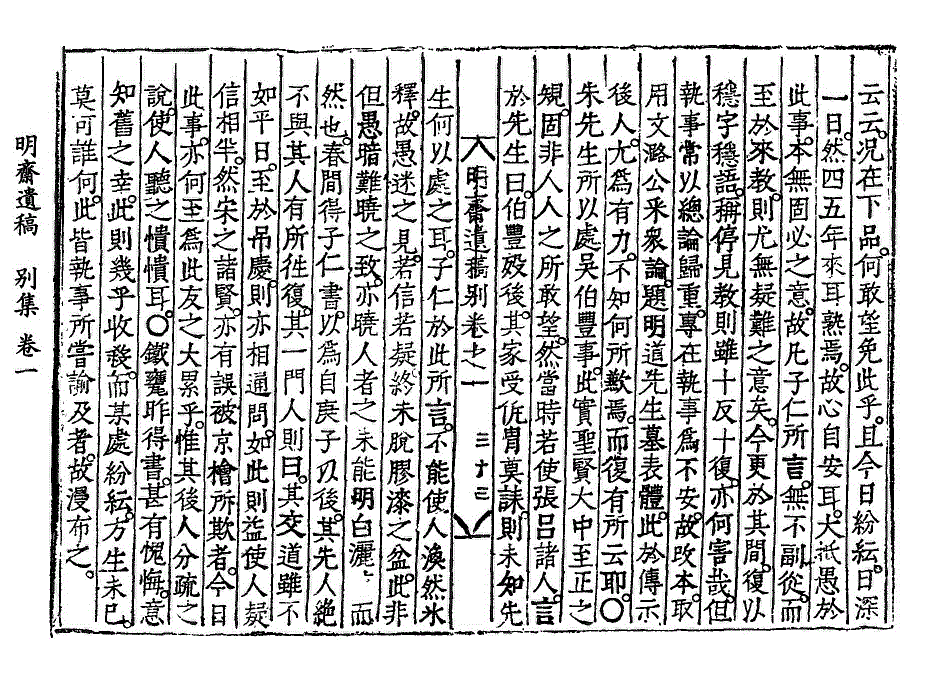 云云。况在下品。何敢望免此乎。且今日纷纭。日深一日。然四五年来耳熟焉。故心自安耳。大抵愚于此事。本无固必之意。故凡子仁所言。无不副从。而至于来教。则尤无疑难之意矣。今更于其间。复以稳字稳语。称停见教则虽十反十复。亦何害哉。但执事常以总论归重。专在执事为不安。故改本。取用文潞公采众论。题明道先生墓表体。此于传示后人。尤为有力。不知何所歉焉。而复有所云耶。○朱先生所以处吴伯丰事。此实圣贤大中至正之规。固非人人之所敢望。然当时若使张吕诸人。言于先生曰。伯丰殁后。其家受侂胄奠诔。则未知先生何以处之耳。子仁于此所言。不能使人涣然冰释。故愚迷之见。若信若疑。终未脱胶漆之盆。此非但愚暗难晓之致。亦晓人者之未能明白洒落而然也。春间得子仁书。以为自庚子以后。其先人绝不与其人有所往复。其一门人则曰。其交道虽不如平日。至于吊庆。则亦相通问。如此则益使人疑信相半。然宋之诸贤。亦有误被京桧所欺者。今日此事。亦何至为此友之大累乎。惟其后人分疏之说。使人听之愦愦耳。○铁瓮昨得书。甚有愧悔。意知旧之幸。此则几乎收杀。而某处纷纭。方生未已。莫可谁何。此皆执事所尝谕及者。故漫布之。
云云。况在下品。何敢望免此乎。且今日纷纭。日深一日。然四五年来耳熟焉。故心自安耳。大抵愚于此事。本无固必之意。故凡子仁所言。无不副从。而至于来教。则尤无疑难之意矣。今更于其间。复以稳字稳语。称停见教则虽十反十复。亦何害哉。但执事常以总论归重。专在执事为不安。故改本。取用文潞公采众论。题明道先生墓表体。此于传示后人。尤为有力。不知何所歉焉。而复有所云耶。○朱先生所以处吴伯丰事。此实圣贤大中至正之规。固非人人之所敢望。然当时若使张吕诸人。言于先生曰。伯丰殁后。其家受侂胄奠诔。则未知先生何以处之耳。子仁于此所言。不能使人涣然冰释。故愚迷之见。若信若疑。终未脱胶漆之盆。此非但愚暗难晓之致。亦晓人者之未能明白洒落而然也。春间得子仁书。以为自庚子以后。其先人绝不与其人有所往复。其一门人则曰。其交道虽不如平日。至于吊庆。则亦相通问。如此则益使人疑信相半。然宋之诸贤。亦有误被京桧所欺者。今日此事。亦何至为此友之大累乎。惟其后人分疏之说。使人听之愦愦耳。○铁瓮昨得书。甚有愧悔。意知旧之幸。此则几乎收杀。而某处纷纭。方生未已。莫可谁何。此皆执事所尝谕及者。故漫布之。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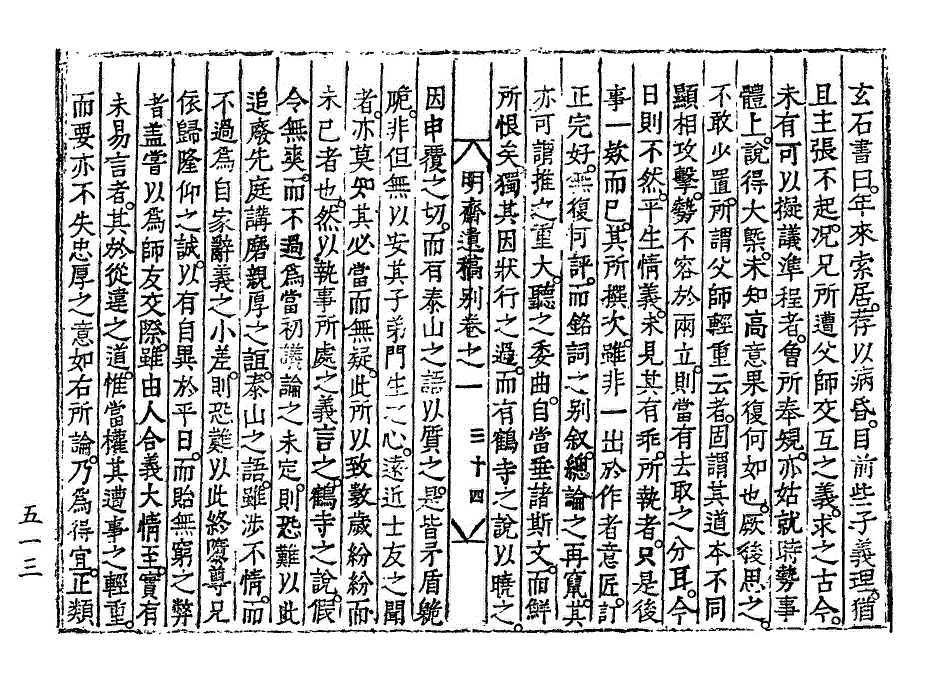 玄石书曰。年来索居。荐以病昏。目前些子义理。犹且主张不起。况兄所遭父师交互之义。求之古今。未有可以拟议准程者。曾所奉规。亦姑就时势事体上。说得大槩。未知高意果复何如也。厥后思之。不敢少置。所谓父师轻重云者。固谓其道本不同显相攻击。势不容于两立。则当有去取之分耳。今日则不然。平生情义。未见其有乖。所执者。只是后事一款而已。其所撰次。虽非一出于作者意匠。订正完好。无复可评。而铭词之别叙。总论之再窜。其亦可谓推之重大。听之委曲。自当垂诸斯文。而鲜所恨矣。独其因状行之过。而有鹤寺之说以晓之。因申覆之切。而有泰山之语以质之。是皆矛盾臲卼。非但无以安其子弟门生之心。远近士友之闻者。亦莫知其必当而无疑。此所以致数岁纷纷而未已者也。然以执事所处之义言之。鹤寺之说。假令无爽。而不过为当初议论之未定。则恐难以此追废先庭讲磨亲厚之谊。泰山之语。虽涉不情。而不过为自家辞义之小差。则恐难以此终隳尊兄依归隆仰之诚。以有自异于平日。而贻无穷之弊者。盖尝以为师友交际。虽由人合义大情至。实有未易言者。其于从违之道。惟当权其遭事之轻重。而要亦不失忠厚之意如右所论。乃为得宜。正类
玄石书曰。年来索居。荐以病昏。目前些子义理。犹且主张不起。况兄所遭父师交互之义。求之古今。未有可以拟议准程者。曾所奉规。亦姑就时势事体上。说得大槩。未知高意果复何如也。厥后思之。不敢少置。所谓父师轻重云者。固谓其道本不同显相攻击。势不容于两立。则当有去取之分耳。今日则不然。平生情义。未见其有乖。所执者。只是后事一款而已。其所撰次。虽非一出于作者意匠。订正完好。无复可评。而铭词之别叙。总论之再窜。其亦可谓推之重大。听之委曲。自当垂诸斯文。而鲜所恨矣。独其因状行之过。而有鹤寺之说以晓之。因申覆之切。而有泰山之语以质之。是皆矛盾臲卼。非但无以安其子弟门生之心。远近士友之闻者。亦莫知其必当而无疑。此所以致数岁纷纷而未已者也。然以执事所处之义言之。鹤寺之说。假令无爽。而不过为当初议论之未定。则恐难以此追废先庭讲磨亲厚之谊。泰山之语。虽涉不情。而不过为自家辞义之小差。则恐难以此终隳尊兄依归隆仰之诚。以有自异于平日。而贻无穷之弊者。盖尝以为师友交际。虽由人合义大情至。实有未易言者。其于从违之道。惟当权其遭事之轻重。而要亦不失忠厚之意如右所论。乃为得宜。正类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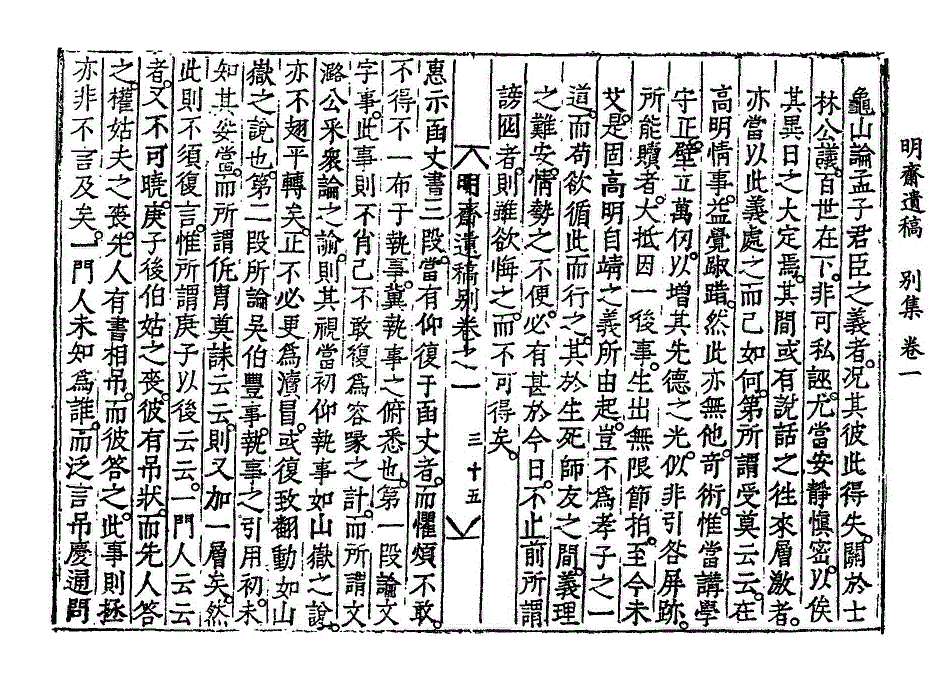 龟山论孟子君臣之义者。况其彼此得失。关于士林公议。百世在下。非可私诬。尤当安静慎密。以俟其异日之大定焉。其间或有说话之往来层激者。亦当以此义处之而已如何。第所谓受奠云云。在高明情事。益觉踧踖。然此亦无他奇术。惟当讲学守正。壁立万仞。以增其先德之光。似非引咎屏迹。所能赎者。大抵因一后事。生出无限节拍。至今未艾。是固高明自靖之义所由起。岂不为孝子之一道。而苟欲循此而行之。其于生死师友之间。义理之难安。情势之不便。必有甚于今日。不止前所谓谤囮者。则虽欲悔之。而不可得矣。
龟山论孟子君臣之义者。况其彼此得失。关于士林公议。百世在下。非可私诬。尤当安静慎密。以俟其异日之大定焉。其间或有说话之往来层激者。亦当以此义处之而已如何。第所谓受奠云云。在高明情事。益觉踧踖。然此亦无他奇术。惟当讲学守正。壁立万仞。以增其先德之光。似非引咎屏迹。所能赎者。大抵因一后事。生出无限节拍。至今未艾。是固高明自靖之义所由起。岂不为孝子之一道。而苟欲循此而行之。其于生死师友之间。义理之难安。情势之不便。必有甚于今日。不止前所谓谤囮者。则虽欲悔之。而不可得矣。惠示函丈书三段。当有仰复于函丈者。而惧烦不敢。不得不一布于执事。冀执事之俯悉也。第一段论文字事。此事则不肖已不敢复为容喙之计。而所谓文潞公采众论之谕。则其视当初仰执事如山岳之说。亦不翅平转矣。正不必更为渎冒。或复致翻动如山岳之说也。第二段所论吴伯丰事。执事之引用初。未知其妥当。而所谓侂胄奠诔云云。则又加一层矣。然此则不须复言。惟所谓庚子以后云云。一门人云云者。又不可晓。庚子后伯姑之丧。彼有吊状。而先人答之。权姑夫之丧。先人有书相吊。而彼答之。此事则拯亦非不言及矣。一门人未知为谁。而泛言吊庆通问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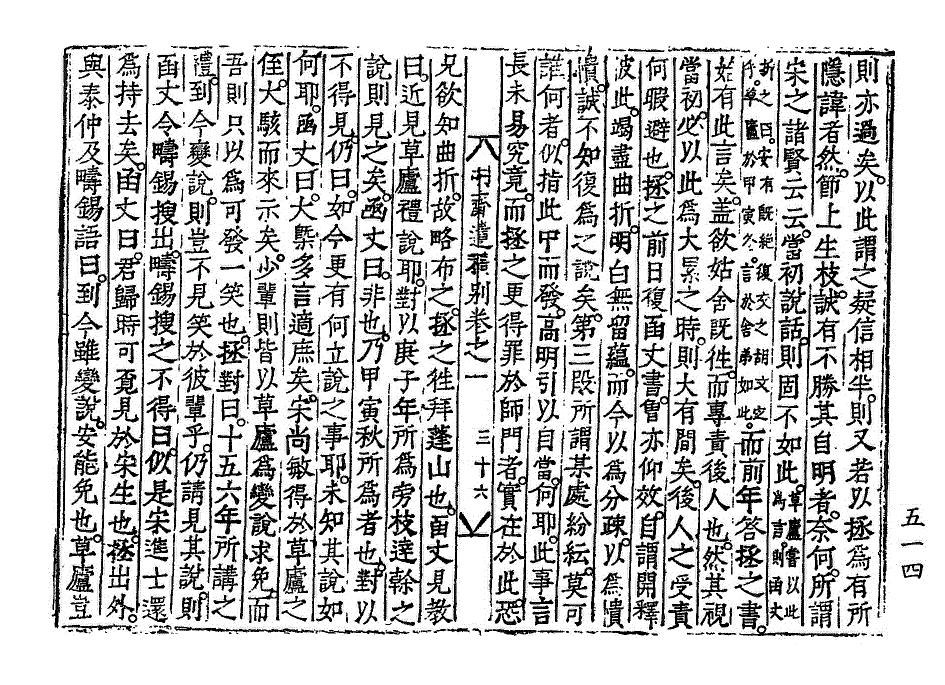 则亦过矣。以此谓之疑信相半。则又若以拯为有所隐讳者然。节上生枝。诚有不胜其自明者。奈何。所谓宋之诸贤云云。当初说话。则固不如此。(草庐尝以此为言。则函丈折之曰。安有既绝复交之胡文定乎。草卢于甲寅冬。言于舍弟如此。)而前年答拯之书。始有此言矣。盖欲姑舍既往。而专责后人也。然其视当初。必以此为大累之时。则大有间矣。后人之受责何暇避也。拯之前日复函丈书。曾亦仰效。自谓开释彼此。竭尽曲折。明白无留蕴。而今以为分疏。以为愦愦。诚不知复为之说矣。第三段所谓某处纷纭。莫可谁何者。似指此中而发。高明引以自当。何耶。此事言长未易究竟。而拯之更得罪于师门者。实在于此。恐兄欲知曲折。故略布之。拯之往拜蓬山也。函丈见教曰。近见草庐礼说耶。对以庚子年所为旁枝达干之说则见之矣。函丈曰。非也。乃甲寅秋所为者也。对以不得见。仍曰。如今更有何立说之事耶。未知其说如何耶。函丈曰。大槩多言适庶矣。宋尚敏得于草庐之侄。大骇而来示矣。少辈则皆以草庐为变说求免。而吾则只以为可发一笑也。拯对曰。十五六年所讲之礼。到今变说。则岂不见笑于彼辈乎。仍请见其说。则函丈令畴锡搜出。畴锡搜之不得曰。似是宋进士还为持去矣。函丈曰。君归时可觅见于宋生也。拯出外。与泰仲及畴锡语曰。到今虽变说。安能免也。草庐岂
则亦过矣。以此谓之疑信相半。则又若以拯为有所隐讳者然。节上生枝。诚有不胜其自明者。奈何。所谓宋之诸贤云云。当初说话。则固不如此。(草庐尝以此为言。则函丈折之曰。安有既绝复交之胡文定乎。草卢于甲寅冬。言于舍弟如此。)而前年答拯之书。始有此言矣。盖欲姑舍既往。而专责后人也。然其视当初。必以此为大累之时。则大有间矣。后人之受责何暇避也。拯之前日复函丈书。曾亦仰效。自谓开释彼此。竭尽曲折。明白无留蕴。而今以为分疏。以为愦愦。诚不知复为之说矣。第三段所谓某处纷纭。莫可谁何者。似指此中而发。高明引以自当。何耶。此事言长未易究竟。而拯之更得罪于师门者。实在于此。恐兄欲知曲折。故略布之。拯之往拜蓬山也。函丈见教曰。近见草庐礼说耶。对以庚子年所为旁枝达干之说则见之矣。函丈曰。非也。乃甲寅秋所为者也。对以不得见。仍曰。如今更有何立说之事耶。未知其说如何耶。函丈曰。大槩多言适庶矣。宋尚敏得于草庐之侄。大骇而来示矣。少辈则皆以草庐为变说求免。而吾则只以为可发一笑也。拯对曰。十五六年所讲之礼。到今变说。则岂不见笑于彼辈乎。仍请见其说。则函丈令畴锡搜出。畴锡搜之不得曰。似是宋进士还为持去矣。函丈曰。君归时可觅见于宋生也。拯出外。与泰仲及畴锡语曰。到今虽变说。安能免也。草庐岂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5H 页
 不知此乎。泰仲曰。以此长城叔父。则以草为失性矣。及归过苏堤。与宋子慎语此曰。若到今变说。则岂不为彼辈所笑乎。子慎笑曰。非但彼辈笑之。此辈亦笑之矣。遂觅礼说。则淳锡出诸其囊中而示之。既见殊不知有变说处。归而以书复于函丈曰。得见草丈礼说。非变说也。只彼以庶字为罪。故特解之曰。我亦非以为庶也。只谓以庶为适云尔。盖主于发明而已。到今发明有何补也。真下教所谓可发二笑者也。函丈不复见答。而草丈之谤。则浸闻矣。一日草丈之侄李上庠𩒮。来见言其礼说。曾与尤翁往复者。而今以变说见谤。未可晓也。仍有多少说话。未几草丈书至。以死期将至。失常可忧等语。指斥函丈。又未几长书又至。并送其礼说矣。拯于进见之时。不曾闻有往复之事。又泰仲,畴锡,子慎之言如右。而草丈之称冤如此。实不能无疑于其间。又草丈书有致书于函丈。而不见答之语。妄意函丈之复书开释为是当。故遂作书于函丈。略问草丈到此之由。且及当有报答之意矣。函丈书来。殊无保合之望。且礼说一款。则于私心。亦终不能无疑。不免又有一书毕陈妄见。而函丈答书殊草草。旋闻宋秀甫以情外之言。大加疑诮。于是遂不敢复言其事。以至于今矣。此事之本末如此而已。彼此三书。誊在别纸。一览而还之。虽子弟勿令见之。
不知此乎。泰仲曰。以此长城叔父。则以草为失性矣。及归过苏堤。与宋子慎语此曰。若到今变说。则岂不为彼辈所笑乎。子慎笑曰。非但彼辈笑之。此辈亦笑之矣。遂觅礼说。则淳锡出诸其囊中而示之。既见殊不知有变说处。归而以书复于函丈曰。得见草丈礼说。非变说也。只彼以庶字为罪。故特解之曰。我亦非以为庶也。只谓以庶为适云尔。盖主于发明而已。到今发明有何补也。真下教所谓可发二笑者也。函丈不复见答。而草丈之谤。则浸闻矣。一日草丈之侄李上庠𩒮。来见言其礼说。曾与尤翁往复者。而今以变说见谤。未可晓也。仍有多少说话。未几草丈书至。以死期将至。失常可忧等语。指斥函丈。又未几长书又至。并送其礼说矣。拯于进见之时。不曾闻有往复之事。又泰仲,畴锡,子慎之言如右。而草丈之称冤如此。实不能无疑于其间。又草丈书有致书于函丈。而不见答之语。妄意函丈之复书开释为是当。故遂作书于函丈。略问草丈到此之由。且及当有报答之意矣。函丈书来。殊无保合之望。且礼说一款。则于私心。亦终不能无疑。不免又有一书毕陈妄见。而函丈答书殊草草。旋闻宋秀甫以情外之言。大加疑诮。于是遂不敢复言其事。以至于今矣。此事之本末如此而已。彼此三书。誊在别纸。一览而还之。虽子弟勿令见之。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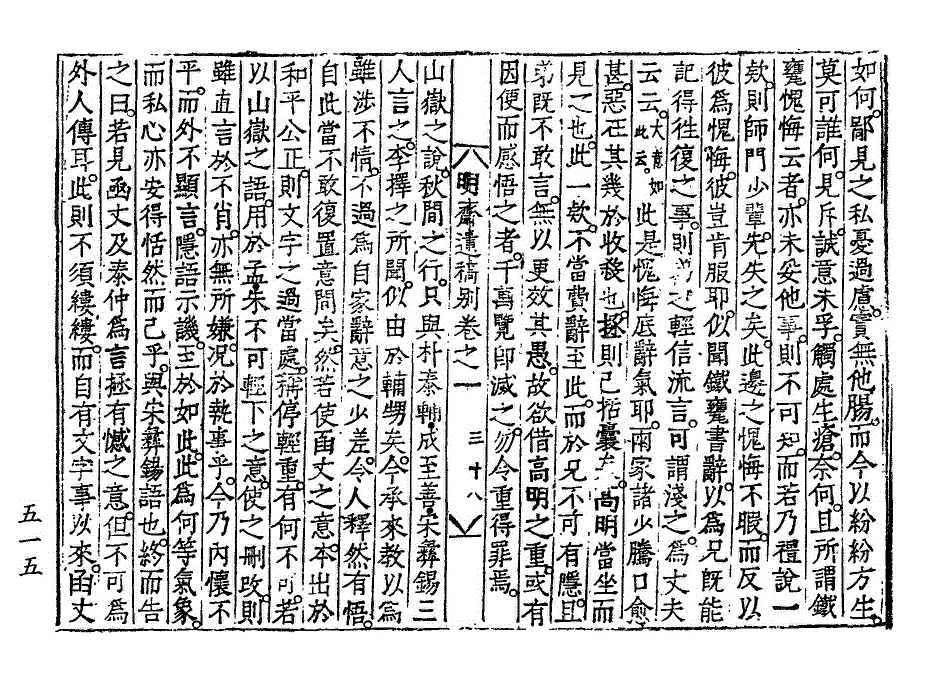 如何。鄙见之私忧过虑。实无他肠。而今以纷纷方生。莫可谁何。见斥。诚意未孚。触处生疮。奈何。且所谓铁瓮愧悔云者。亦未妥他事。则不可知。而若乃礼说一款。则师门少辈。先失之矣。此边之愧悔不暇。而反以彼为愧悔。彼岂肯服耶。似闻铁瓮书辞。以为兄既能记得往复之事。则为之轻信流言。可谓浅之。为丈夫云云。(大意如此云。)此是愧悔底辞气耶。两家诸少腾口愈甚。恶在其几于收杀也。拯则已括囊矣。高明当坐而见之也。此一款。不当费辞至此。而于兄不可有隐。且弟既不敢言。无以更效其愚。故欲借高明之重。或有因便而感悟之者。千万览即灭之。勿令重得罪焉。
如何。鄙见之私忧过虑。实无他肠。而今以纷纷方生。莫可谁何。见斥。诚意未孚。触处生疮。奈何。且所谓铁瓮愧悔云者。亦未妥他事。则不可知。而若乃礼说一款。则师门少辈。先失之矣。此边之愧悔不暇。而反以彼为愧悔。彼岂肯服耶。似闻铁瓮书辞。以为兄既能记得往复之事。则为之轻信流言。可谓浅之。为丈夫云云。(大意如此云。)此是愧悔底辞气耶。两家诸少腾口愈甚。恶在其几于收杀也。拯则已括囊矣。高明当坐而见之也。此一款。不当费辞至此。而于兄不可有隐。且弟既不敢言。无以更效其愚。故欲借高明之重。或有因便而感悟之者。千万览即灭之。勿令重得罪焉。山岳之说。秋间之行。只与朴泰辅,成至善,宋彝锡三人言之。李择之所闻。似由于辅甥矣。今承来教以为虽涉不情。不过为自家辞意之少差。令人释然有悟。自此当不敢复置意间矣。然若使函丈之意。本出于和平公正。则文字之过当处。称停轻重。有何不可。若以山岳之语。用于孟,朱不可轻下之意。使之删改。则虽直言于不肖。亦无所嫌。况于执事乎。今乃内怀不平。而外不显言。隐语示讥。至于如此。此为何等气象。而私心亦安得恬然而已乎。与宋彝锡语也。终而告之曰。若见函丈及泰仲为言拯有憾之意。但不可为外人传耳。此则不须缕缕。而自有文字事以来。函丈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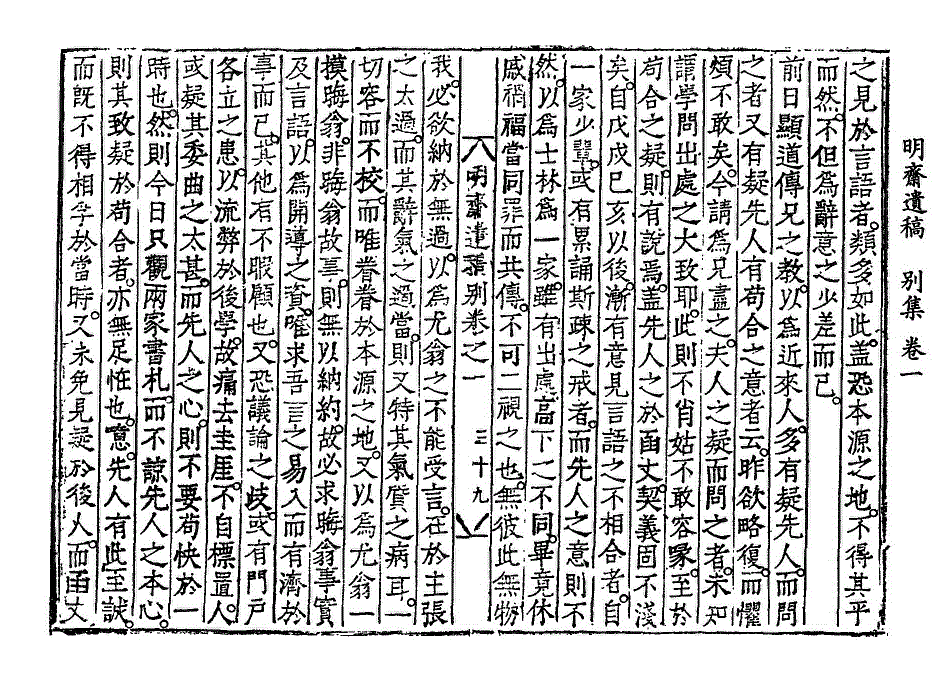 之见于言语者。类多如此。盖恐本源之地。不得其平而然。不但为辞意之少差而已。
之见于言语者。类多如此。盖恐本源之地。不得其平而然。不但为辞意之少差而已。前日显道传兄之教。以为近来人。多有疑先人。而问之者又有疑先人有苟合之意者云。昨欲略复。而惧烦不敢矣。今请为兄尽之。夫人之疑而问之者。未知谓学问出处之大致耶。此则不肖姑不敢容喙。至于苟合之疑。则有说焉。盖先人之于函丈。契义固不浅矣。自戊戌己亥以后。渐有意见言语之不相合者。自一家少辈。或有累诵斯疏之戒者。而先人之意则不然。以为士林为一家。虽有出处高下之不同。毕竟休戚祸福当同罪而共传。不可二视之也。无彼此无物我。必欲纳于无过。以为尤翁之不能受言。在于主张之太过。而其辞气之过当。则又特其气质之病耳。一切容而不校。而唯眷眷于本源之地。又以为尤翁一摸晦翁。非晦翁故事。则无以纳约。故必求晦翁事实及言语。以为开导之资。唯求吾言之易入而有济于事而已。其他有不暇顾也。又恐议论之岐。或有门户各立之患。以流弊于后学。故痛去圭厓。不自标置。人或疑其委曲之太甚。而先人之心。则不要苟快于一时也。然则今日只观两家书札。而不谅先人之本心。则其致疑于苟合者。亦无足怪也。噫。先人有此至诚。而既不得相孚于当时。又未免见疑于后人。而函丈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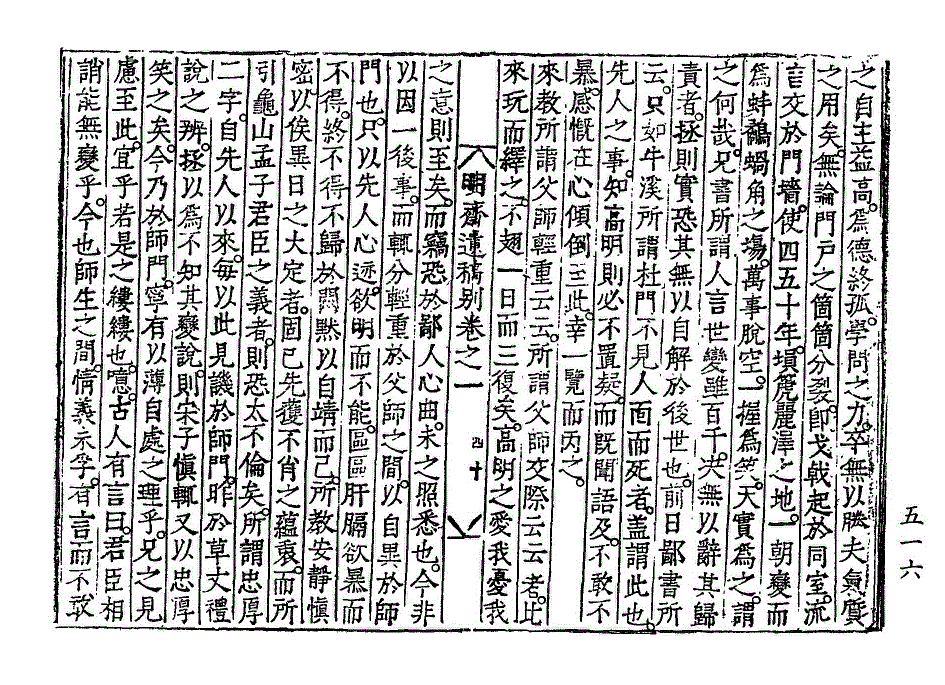 之自主益高。为德终孤。学问之力。卒无以胜夫气质之用矣。无论门户之个个分裂。即戈戟起于同室。流言交于门墙。使四五十年。埙篪丽泽之地。一朝变而为蚌鹬蜗角之场。万事脱空。一握为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兄书所谓人言世变虽百千。决无以辞其归责者。拯则实恐其无以自解于后世也。前日鄙书所云。只如牛溪所谓杜门不见人面而死者。盖谓此也。先人之事。知高明则必不置疑。而既闻语及。不敢不暴。感慨在心。倾倒至此。幸一览而丙之。
之自主益高。为德终孤。学问之力。卒无以胜夫气质之用矣。无论门户之个个分裂。即戈戟起于同室。流言交于门墙。使四五十年。埙篪丽泽之地。一朝变而为蚌鹬蜗角之场。万事脱空。一握为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兄书所谓人言世变虽百千。决无以辞其归责者。拯则实恐其无以自解于后世也。前日鄙书所云。只如牛溪所谓杜门不见人面而死者。盖谓此也。先人之事。知高明则必不置疑。而既闻语及。不敢不暴。感慨在心。倾倒至此。幸一览而丙之。来教所谓父师轻重云云。所谓父师交际云云者。比来玩而绎之。不翅一日而三复矣。高明之爱我忧我之意则至矣。而窃恐于鄙人心曲。未之照悉也。今非以因一后事。而辄分轻重于父师之间。以自异于师门也。只以先人心迹。欲明而不能。区区肝膈欲暴而不得。终不得不归于闷默以自靖而已。所教安静慎密。以俟异日之大定者。固已先获不肖之蕴衷。而所引龟山孟子君臣之义者。则恐太不伦矣。所谓忠厚二字。自先人以来。每以此见讥于师门。昨于草丈礼说之辨。拯以为不知其变说。则宋子慎辄又以忠厚笑之矣。今乃于师门。宁有以薄自处之理乎。兄之见虑至此。宜乎若是之缕缕也。噫。古人有言曰。君臣相诮能无变乎。今也师生之间。情义未孚。有言而不敢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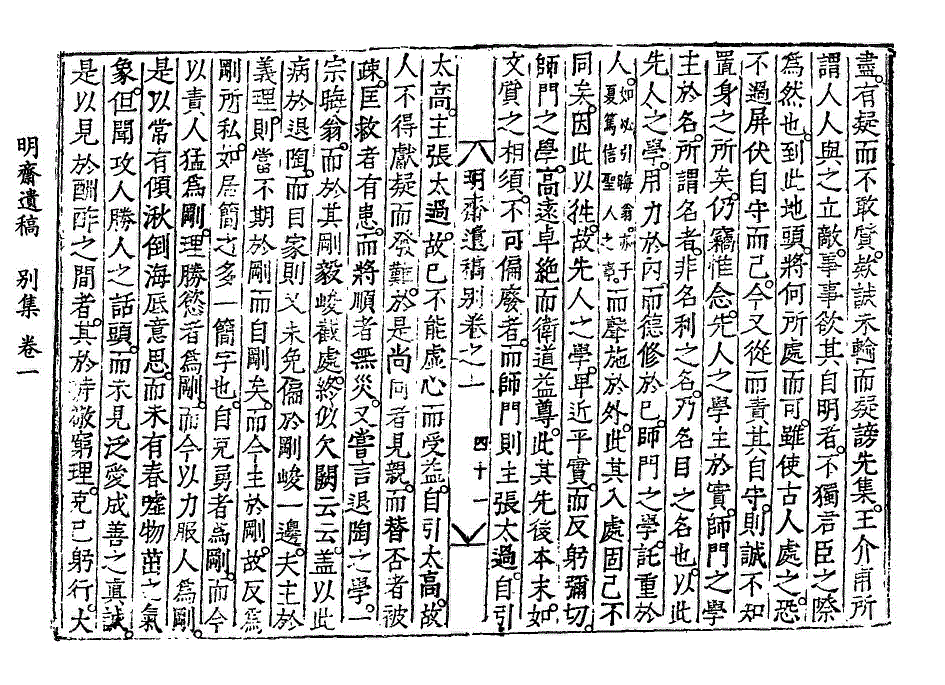 尽。有疑而不敢质。款诚未输而疑谤先集。王介甫所谓人人与之立敌。事事欲其自明者。不独君臣之际为然也。到此地头。将何所处而可。虽使古人处之。恐不过屏伏自守而已。今又从而责其自守。则诚不知置身之所矣。仍窃惟念。先人之学主于实。师门之学主于名。所谓名者。非名利之名。乃名目之名也。以此先人之学。用力于内而德修于己。师门之学。托重于人。(如必引晦翁。亦子夏笃信圣人之事。)而声施于外。此其入处固已不同矣。因此以往。故先人之学。卑近平实而反躬弥切。师门之学。高远卓绝而卫道益尊。此其先后本末。如文质之相须。不可偏废者。而师门则主张太过。自引,太高。主张太过。故己不能虚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献疑而发难。于是尚同者见亲。而替否者被疏。匡救者有患。而将顺者无灾。又尝言退陶之学。一宗晦翁。而于其刚毅峻截处。终似欠阙云云。盖以此病于退陶。而自家则又未免偏于刚峻一边。夫主于义理。则当不期于刚而自刚矣。而今主于刚。故反为刚所私。如居简之多一简字也。自克勇者为刚。而今以责人猛为刚。理胜欲者为刚。而今以力服人为刚。是以常有倾湫倒海底意思。而未有春嘘物茁之气象。但闻攻人胜人之话头。而未见泛爱成善之真诚。是以见于酬酢之间者。其于持敬穷理。克己躬行。大
尽。有疑而不敢质。款诚未输而疑谤先集。王介甫所谓人人与之立敌。事事欲其自明者。不独君臣之际为然也。到此地头。将何所处而可。虽使古人处之。恐不过屏伏自守而已。今又从而责其自守。则诚不知置身之所矣。仍窃惟念。先人之学主于实。师门之学主于名。所谓名者。非名利之名。乃名目之名也。以此先人之学。用力于内而德修于己。师门之学。托重于人。(如必引晦翁。亦子夏笃信圣人之事。)而声施于外。此其入处固已不同矣。因此以往。故先人之学。卑近平实而反躬弥切。师门之学。高远卓绝而卫道益尊。此其先后本末。如文质之相须。不可偏废者。而师门则主张太过。自引,太高。主张太过。故己不能虚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献疑而发难。于是尚同者见亲。而替否者被疏。匡救者有患。而将顺者无灾。又尝言退陶之学。一宗晦翁。而于其刚毅峻截处。终似欠阙云云。盖以此病于退陶。而自家则又未免偏于刚峻一边。夫主于义理。则当不期于刚而自刚矣。而今主于刚。故反为刚所私。如居简之多一简字也。自克勇者为刚。而今以责人猛为刚。理胜欲者为刚。而今以力服人为刚。是以常有倾湫倒海底意思。而未有春嘘物茁之气象。但闻攻人胜人之话头。而未见泛爱成善之真诚。是以见于酬酢之间者。其于持敬穷理。克己躬行。大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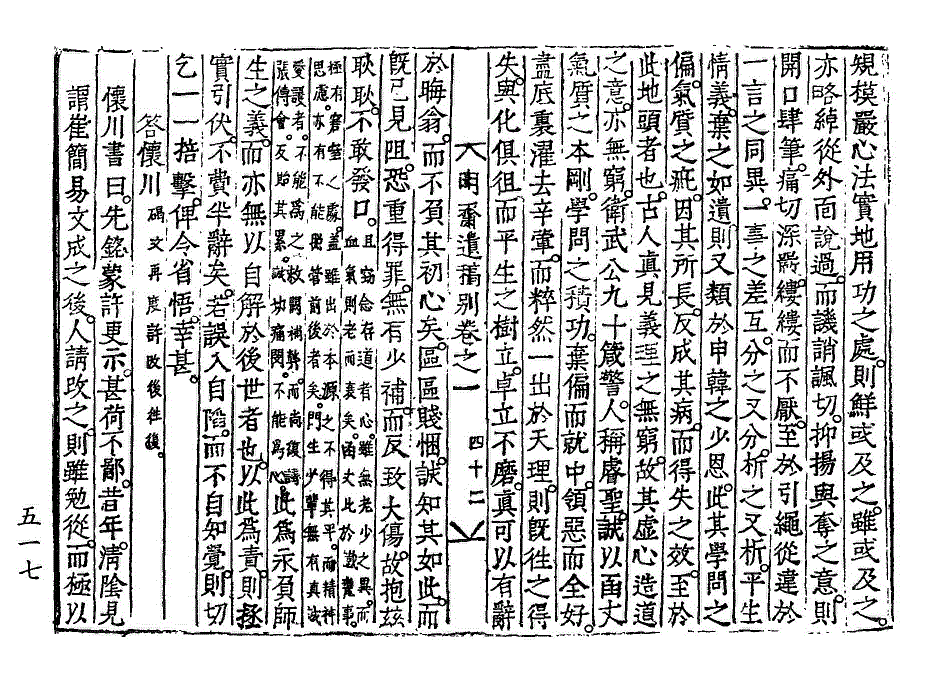 规模严心法实地用功之处。则鲜或及之。虽或及之。亦略绰从外面说过。而讥诮讽切。抑扬与夺之意。则开口肆笔。痛切深严。缕缕而不厌。至于引绳从违于一言之同异。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义。弃之如遗则又类于申韩之少恩。此其学问之偏。气质之疵。因其所长。反成其病。而得失之效。至于此地头者也。古人真见义理之无穷。故其虚心造道之意。亦无穷。卫武公九十箴警。人称睿圣。诚以函丈气质之本刚。学问之积功。弃偏而就中。领恶而全好。尽底里濯去辛荤。而粹然一出于天理。则既往之得失。与化俱徂而平生之树立。卓立不磨。真可以有辞于晦翁。而不负其初心矣。区区贱悃。诚知其如此。而既已见阻。恐重得罪。无有少补。而反致大伤。故抱玆耿耿。不敢发口。(且窃念存道者心。虽无老少之异。而血气则老而襄矣。函丈此于铁瓮事。极有窘室之处。盖虽出于本源之不得其平。而精神思虑。亦有不能脱管前后者矣。门生少辈无有真诚爱护者。不能为之救阙补弊。而尚复诪张傅会。反贻其累。诚切痛闵。不能为心。)此为永负师生之义。而亦无以自解于后世者也。以此为责。则拯实引伏。不费半辞矣。若误入自陷。而不自知觉。则切乞一一掊击。俾令省悟。幸甚。
规模严心法实地用功之处。则鲜或及之。虽或及之。亦略绰从外面说过。而讥诮讽切。抑扬与夺之意。则开口肆笔。痛切深严。缕缕而不厌。至于引绳从违于一言之同异。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义。弃之如遗则又类于申韩之少恩。此其学问之偏。气质之疵。因其所长。反成其病。而得失之效。至于此地头者也。古人真见义理之无穷。故其虚心造道之意。亦无穷。卫武公九十箴警。人称睿圣。诚以函丈气质之本刚。学问之积功。弃偏而就中。领恶而全好。尽底里濯去辛荤。而粹然一出于天理。则既往之得失。与化俱徂而平生之树立。卓立不磨。真可以有辞于晦翁。而不负其初心矣。区区贱悃。诚知其如此。而既已见阻。恐重得罪。无有少补。而反致大伤。故抱玆耿耿。不敢发口。(且窃念存道者心。虽无老少之异。而血气则老而襄矣。函丈此于铁瓮事。极有窘室之处。盖虽出于本源之不得其平。而精神思虑。亦有不能脱管前后者矣。门生少辈无有真诚爱护者。不能为之救阙补弊。而尚复诪张傅会。反贻其累。诚切痛闵。不能为心。)此为永负师生之义。而亦无以自解于后世者也。以此为责。则拯实引伏。不费半辞矣。若误入自陷。而不自知觉。则切乞一一掊击。俾令省悟。幸甚。答怀川(碣文再度许改后往复。)
怀川书曰。先铭蒙许更示。甚荷不鄙。昔年。清阴见谓崔简易文成之后。人请改之。则虽勉从。而极以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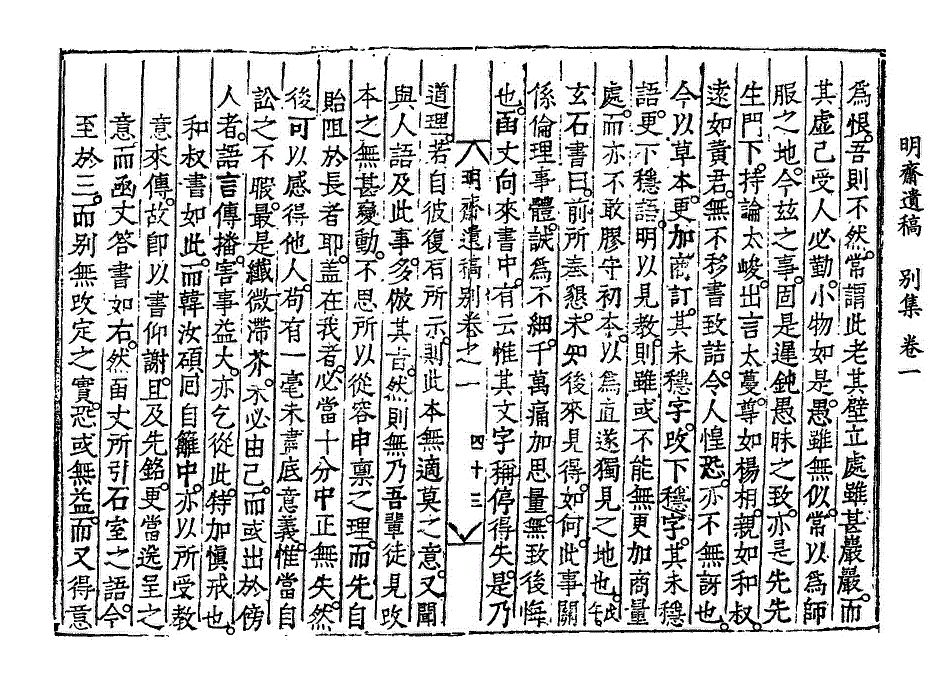 为恨。吾则不然。常谓此老其壁立处虽甚岩岩。而其虚己受人必勤。小物如是。愚虽无似。常以为师服之地。今玆之事。固是迟钝愚昧之致。亦是先先生门下。持论太峻。出言太蔓。尊如杨相。亲如和叔。远如黄君。无不移书致诘。令人惶恐。亦不无讶也。今以草本。更加商订。其未稳字。改下稳字。其未稳语。更下稳语。明以见教。则虽或不能无更加商量处。而亦不敢胶守初本。以为直遂独见之地也。(戊午。)
为恨。吾则不然。常谓此老其壁立处虽甚岩岩。而其虚己受人必勤。小物如是。愚虽无似。常以为师服之地。今玆之事。固是迟钝愚昧之致。亦是先先生门下。持论太峻。出言太蔓。尊如杨相。亲如和叔。远如黄君。无不移书致诘。令人惶恐。亦不无讶也。今以草本。更加商订。其未稳字。改下稳字。其未稳语。更下稳语。明以见教。则虽或不能无更加商量处。而亦不敢胶守初本。以为直遂独见之地也。(戊午。)玄石书曰。前所奉恳。未知后来见得。如何。此事关系伦理事体。诚为不细。千万痛加思量。无致后悔也。函丈向来书中。有云惟其文字称停得失。是乃道理。若自彼复有所示。则此本无适莫之意。又闻与人语及此事。多仿其旨。然则无乃吾辈徒见改本之无甚变动。不思所以从容申禀之理。而先自贻阻于长者耶。盖在我者。必当十分中正无失。然后可以感得他人。苟有一毫未尽底意义。惟当自讼之不暇。最是纤微滞芥。未必由己。而或出于傍人者。语言传播。害事益大。亦乞从此。特加慎戒也。
和叔书如此。而韩汝硕回自篱中。亦以所受教意来传。故即以书仰谢。且及先铭。更当送呈之意而函丈答书如右。然函丈所引石室之语。今至于三。而别无改定之实。恐或无益。而又得意
明斋先生遗稿别卷之一 第 5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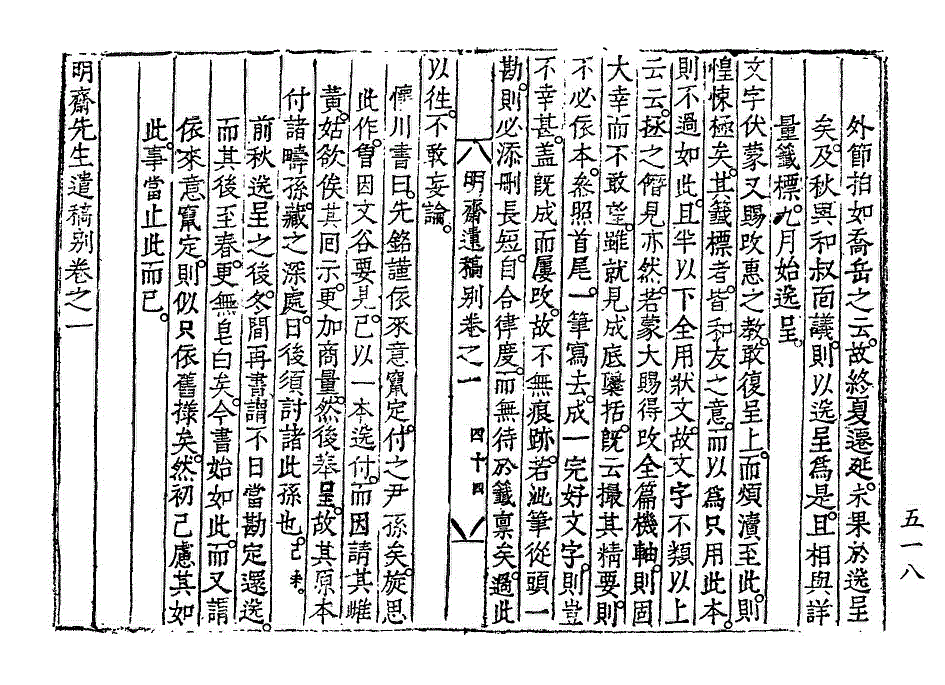 外节拍如乔岳之云。故终夏迁延。未果于送呈矣。及秋与和叔面议。则以送呈为是。且相与详量签标。九月始送呈。
外节拍如乔岳之云。故终夏迁延。未果于送呈矣。及秋与和叔面议。则以送呈为是。且相与详量签标。九月始送呈。文字伏蒙又赐改惠之教。敢复呈上。而烦渎至此。则惶悚极矣。其签标考。皆和友之意。而以为只用此本。则不过如此。且半以下全用状文。故文字不类以上云云。拯之僭见亦然。若蒙大赐得改全篇机轴。则固大幸而不敢望。虽就见成底檃括。既云撮其精要。则不必依本。参照首尾。一笔写去。成一完好文字。则岂不幸甚。盖既成而屡改。故不无痕迹。若泚笔从头一勘。则必添删长短。自合律度。而无待于签禀矣。过此以往。不敢妄论。
怀川书曰。先铭谨依来意窜定。付之尹孙矣。旋思此作。曾因文谷要见。已以一本送付。而因请其雌黄。姑欲俟其回示。更加商量。然后奉呈。故其原本付诸畴孙。藏之深处。日后须讨诸此孙也。(己未。)
前秋送呈之后。冬间再书谓不日当勘定还送。而其后至春。更无皀白矣。今书始如此。而又谓依来意窜定。则似只依旧样矣。然初已虑其如此。事当止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