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x 页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书(七首)
书(七首)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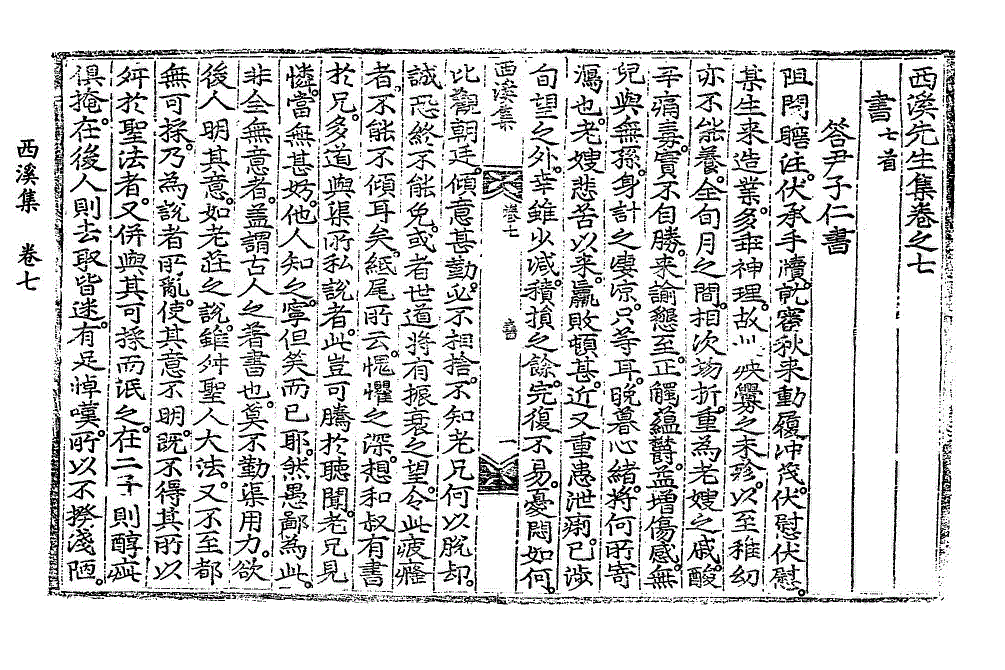 答尹子仁书
答尹子仁书阻问瞻注。伏承手牍。就审秋来动履冲茂。伏慰伏慰。某生来造业。多乖神理。故此殃衅之未殄。以至稚幼亦不能养全。旬月之间。相次殁折。重为老嫂之戚。酸辛痛毒。实不自胜。来谕恳至。正触蕴郁。益增伤感。无儿与无孙。身计之凄凉。只等耳。晚暮心绪。将何所寄泻也。老嫂悲苦以来。羸败顿甚。近又重患泄痢。已涉旬望之外。幸虽少减。积损之馀。完复不易。忧闷如何。比观朝廷。倾意甚勤。必不相舍。不知老兄何以脱却。诚恐终不能免。或者世道将有振衰之望。令此疲癃者。不能不倾耳矣。纸尾所云。愧惧之深。想和叔有书于兄。多道与渠所私说者。此岂可腾于听闻。老兄见怜。当无甚妨。他人知之。宁但笑而已耶。然愚鄙为此。非全无意者。盖谓古人之著书也。莫不勤渠用力。欲后人明其意。如老庄之说。虽舛圣人大法。又不至都无可采。乃为说者所乱。使其意不明。既不得其所以舛于圣法者。又并与其可采而泯之。在二子则醇疵俱掩。在后人则去取皆迷。有足悼叹。所以不揆浅陋。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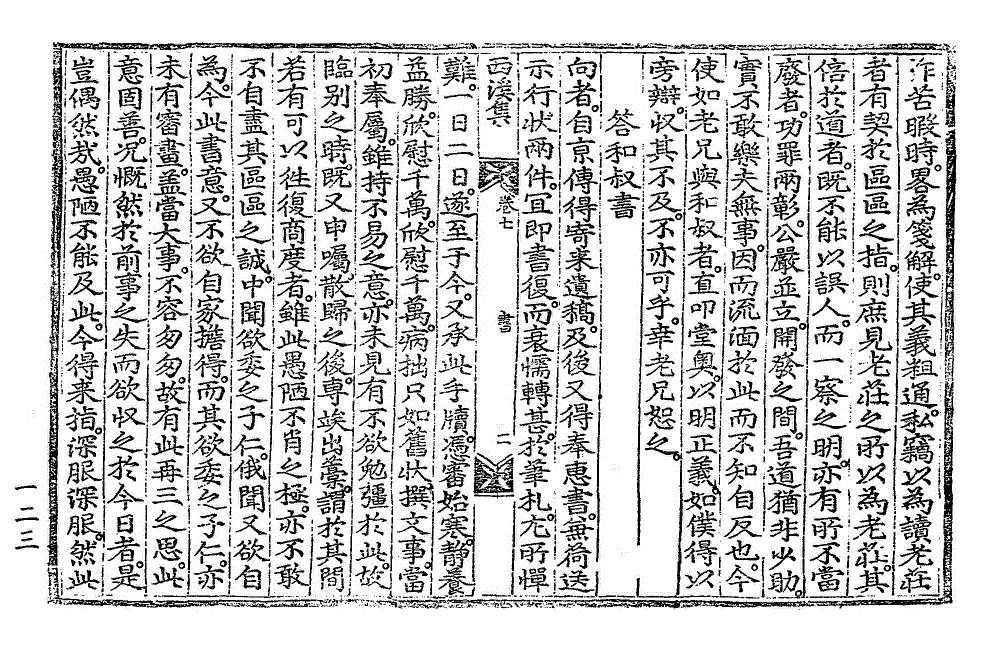 作苦暇时。略为笺解。使其义粗通。私窃以为读老庄者有契于区区之指。则庶见老庄之所以为老庄。其倍于道者。既不能以误人。而一察之明。亦有所不当废者。功罪两彰。公严并立。开发之间。吾道犹非少助。实不敢乐夫无事。因而流湎于此而不知自反也。今使如老兄与和叔者。直叩堂奥。以明正义。如仆得以旁辩。收其不及。不亦可乎。幸老兄恕之。
作苦暇时。略为笺解。使其义粗通。私窃以为读老庄者有契于区区之指。则庶见老庄之所以为老庄。其倍于道者。既不能以误人。而一察之明。亦有所不当废者。功罪两彰。公严并立。开发之间。吾道犹非少助。实不敢乐夫无事。因而流湎于此而不知自反也。今使如老兄与和叔者。直叩堂奥。以明正义。如仆得以旁辩。收其不及。不亦可乎。幸老兄恕之。答和叔书
向者。自京传得寄来遗稿。及后又得奉惠书。兼荷送示行状两件。宜即书复。而衰懦转甚。于笔札。尤所惮难。一日二日。遂至于今。又承此手牍。凭审始寒。静养益胜。欣慰千万。欣慰千万。病拙只如旧状。撰文事。当初奉属。虽持不易之意。亦未见有不欲勉彊于此。故临别之时。既又申嘱。散归之后。专俟出藁。谓于其间若有可以往复商度者。虽此愚陋不肖之极。亦不敢不自尽其区区之诚。中闻欲委之子仁。俄闻又欲自为。今此书意。又不欲自家担得。而其欲委之子仁。亦未有审画。盖当大事。不容悤悤。故有此再三之思。此意固善。况慨然于前事之失而欲收之于今日者。是岂偶然哉。愚陋不能及此。今得来指。深服深服。然此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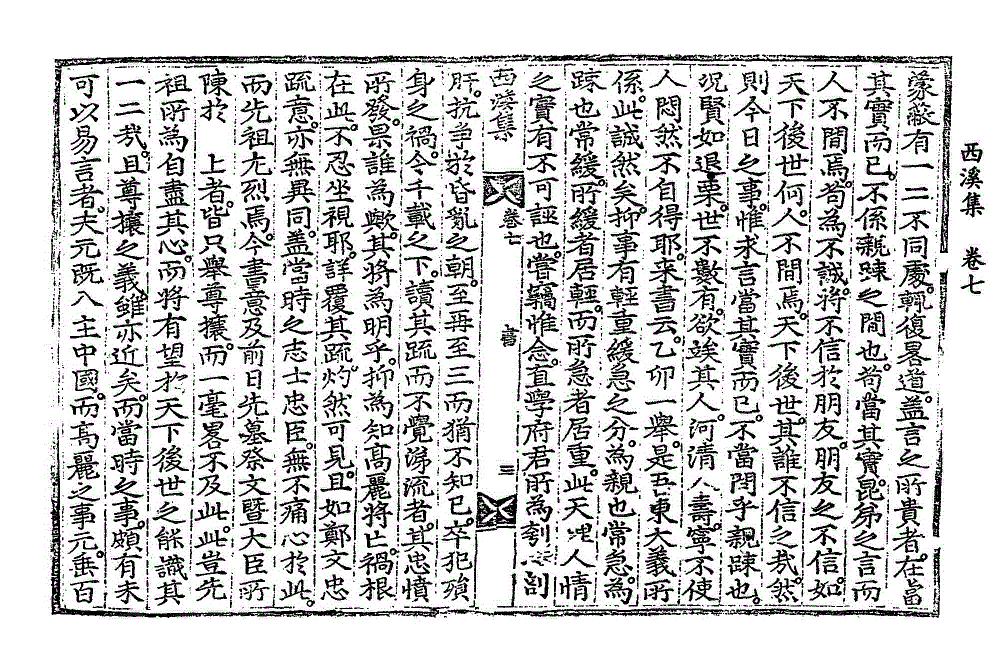 蒙蔽有一二不同处。辄复略道。盖言之所贵者。在当其实而已。不系亲疏之间也。苟当其实。昆弟之言而人不间焉。苟为不诚。将不信于朋友。朋友之不信。如天下后世何。人不间焉。天下后世。其谁不信之哉。然则今日之事。惟求言当其实而已。不当问乎亲疏也。况贤如退,栗。世不数有。欲俟其人。河清人寿。宁不使人闷然不自得耶。来书云。乙卯一举。是吾东大义所系。此诚然矣。抑事有轻重缓急之分。为亲也常急。为疏也常缓。所缓者居轻。而所急者居重。此天理人情之实有不可诬也。尝窃惟念。直学府君所为刳心剖肝。抗争于昏乱之朝。至再至三而犹不知己。卒犯殒身之祸。今千载之下。读其疏而不觉涕流者。其忠愤所发。果谁为欤。其将为明乎。抑为知高丽将亡。祸根在此。不忍坐视耶。详覆其疏。灼然可见。且如郑文忠疏意。亦无异同。盖当时之志士忠臣。无不痛心于此。而先祖尤烈焉。今书意及前日先墓祭文暨大臣所陈于 上者。皆只举尊攘。而一毫略不及此。此岂先祖所为自尽其心。而将有望于天下后世之能识其一二哉。且尊攘之义。虽亦近矣。而当时之事。颇有未可以易言者。夫元既入主中国。而高丽之事元。垂百
蒙蔽有一二不同处。辄复略道。盖言之所贵者。在当其实而已。不系亲疏之间也。苟当其实。昆弟之言而人不间焉。苟为不诚。将不信于朋友。朋友之不信。如天下后世何。人不间焉。天下后世。其谁不信之哉。然则今日之事。惟求言当其实而已。不当问乎亲疏也。况贤如退,栗。世不数有。欲俟其人。河清人寿。宁不使人闷然不自得耶。来书云。乙卯一举。是吾东大义所系。此诚然矣。抑事有轻重缓急之分。为亲也常急。为疏也常缓。所缓者居轻。而所急者居重。此天理人情之实有不可诬也。尝窃惟念。直学府君所为刳心剖肝。抗争于昏乱之朝。至再至三而犹不知己。卒犯殒身之祸。今千载之下。读其疏而不觉涕流者。其忠愤所发。果谁为欤。其将为明乎。抑为知高丽将亡。祸根在此。不忍坐视耶。详覆其疏。灼然可见。且如郑文忠疏意。亦无异同。盖当时之志士忠臣。无不痛心于此。而先祖尤烈焉。今书意及前日先墓祭文暨大臣所陈于 上者。皆只举尊攘。而一毫略不及此。此岂先祖所为自尽其心。而将有望于天下后世之能识其一二哉。且尊攘之义。虽亦近矣。而当时之事。颇有未可以易言者。夫元既入主中国。而高丽之事元。垂百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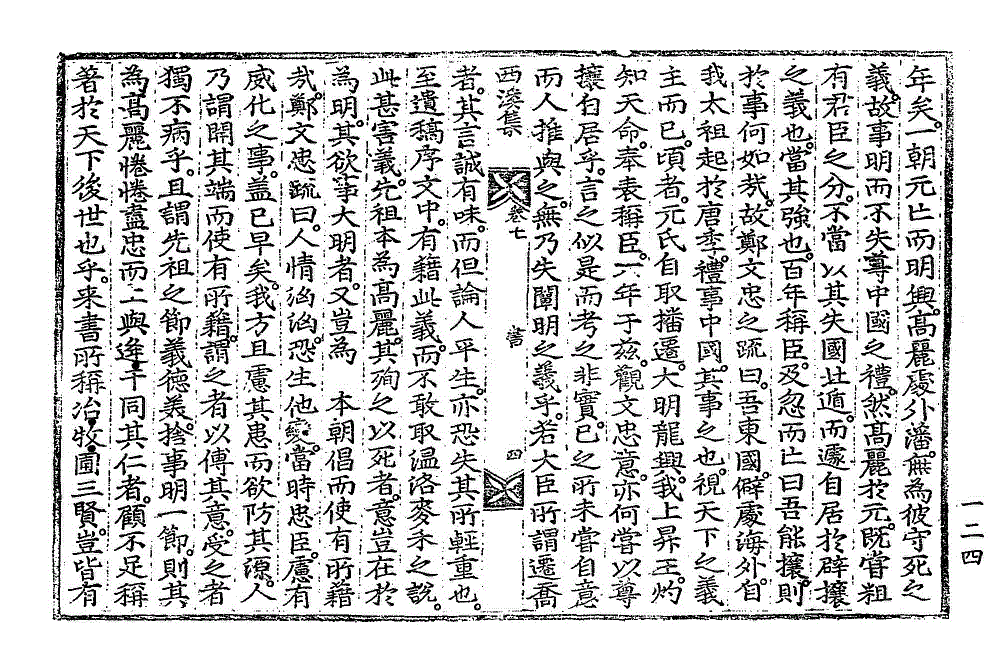 年矣。一朝元亡而明兴。高丽处外潘。无为彼守死之义。故事明而不失尊中国之礼。然高丽于元。既尝粗有君臣之分。不当以其失国北遁。而遽自居于辟攘之义也。当其强也。百年称臣。及忽而亡曰吾能攘。则于事何如哉。故郑文忠之疏曰。吾东国。僻处海外。自我太祖起于唐季。礼事中国。其事之也。视天下之义主而已。顷者。元氏自取播迁。大明龙兴。我上升王。灼知天命。奉表称臣。六年于玆。观文忠意。亦何尝以尊攘白居乎。言之似是而考之非实。己之所未尝自意而人推与之。无乃失阐明之义乎。若大臣所谓迁乔者。其言诚有味。而但论人平生。亦恐失其所轻重也。至遗稿序文中。有藉此义。而不敢取温洛麦禾之说。此甚害义。先祖本为高丽。其殉之以死者。意岂在于为明。其欲事大明者。又岂为 本朝倡而使有所藉哉。郑文忠疏曰。人情汹汹。恐生他变。当时忠臣。虑有威化之事。盖已早矣。我方且宪其患而欲防其源。人乃谓开其端而使有所藉。谓之者以傅其意。受之者独不病乎。且谓先祖之节义德美。舍事明一节。则其为高丽惓惓尽忠而上与逄,干同其仁者。顾不足称著于天下后世也乎。来书所称冶,牧,圃三贤。岂皆有
年矣。一朝元亡而明兴。高丽处外潘。无为彼守死之义。故事明而不失尊中国之礼。然高丽于元。既尝粗有君臣之分。不当以其失国北遁。而遽自居于辟攘之义也。当其强也。百年称臣。及忽而亡曰吾能攘。则于事何如哉。故郑文忠之疏曰。吾东国。僻处海外。自我太祖起于唐季。礼事中国。其事之也。视天下之义主而已。顷者。元氏自取播迁。大明龙兴。我上升王。灼知天命。奉表称臣。六年于玆。观文忠意。亦何尝以尊攘白居乎。言之似是而考之非实。己之所未尝自意而人推与之。无乃失阐明之义乎。若大臣所谓迁乔者。其言诚有味。而但论人平生。亦恐失其所轻重也。至遗稿序文中。有藉此义。而不敢取温洛麦禾之说。此甚害义。先祖本为高丽。其殉之以死者。意岂在于为明。其欲事大明者。又岂为 本朝倡而使有所藉哉。郑文忠疏曰。人情汹汹。恐生他变。当时忠臣。虑有威化之事。盖已早矣。我方且宪其患而欲防其源。人乃谓开其端而使有所藉。谓之者以傅其意。受之者独不病乎。且谓先祖之节义德美。舍事明一节。则其为高丽惓惓尽忠而上与逄,干同其仁者。顾不足称著于天下后世也乎。来书所称冶,牧,圃三贤。岂皆有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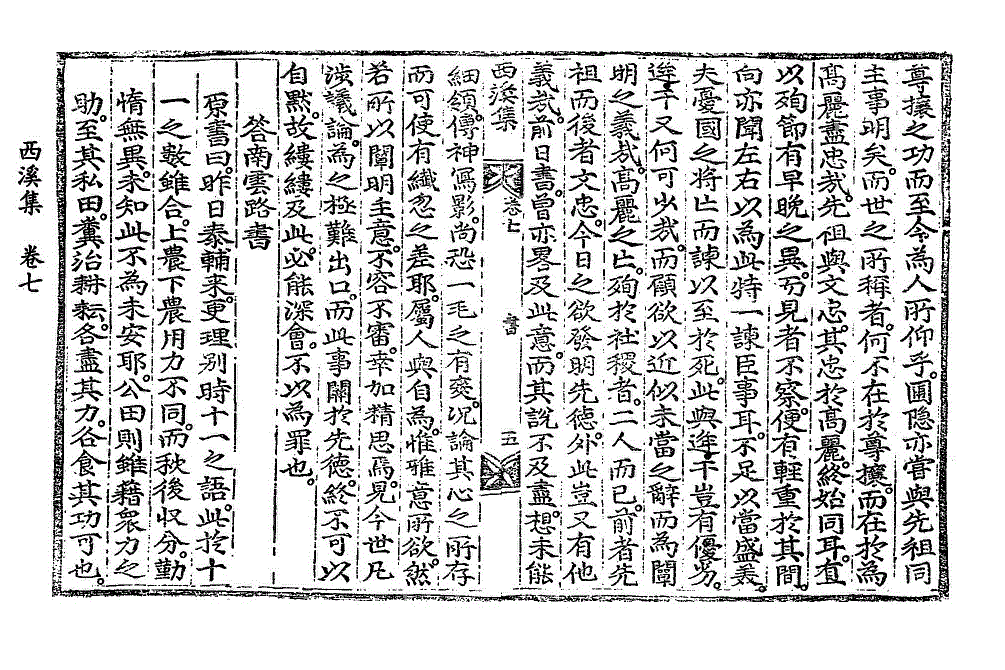 尊攘之功而至今为人所仰乎。圃隐亦尝与先祖同主事明矣。而世之所称者。何不在于尊攘。而在于为高丽尽忠哉。先祖与文忠。其忠于高丽。终始同耳。直以殉节有早晚之异。而见者不察。便有轻重于其间。向亦闻左右以为此特一谏臣事耳。不足以当盛美。夫忧国之将亡而谏以至于死。此与逄,干岂有优劣。逄,干又何可少哉。而顾欲以近似未当之辞而为阐明之义哉。高丽之亡。殉于社稷者。二人而已。前者先祖而后者文忠。今日之欲发明先德。外此岂又有他义哉。前日书。曾亦略及此意。而其说不及尽。想未能细领。传神写影。尚恐一毛之有爽。况论其心之所存而可使有纤忽之差耶。属人与自为。惟雅意所欲。然若所以阐明主意。不容不审。幸加精思焉。见今世凡涉议论。为之极难出口。而此事关于先德。终不可以自默。故缕缕及此。必能深会。不以为罪也。
尊攘之功而至今为人所仰乎。圃隐亦尝与先祖同主事明矣。而世之所称者。何不在于尊攘。而在于为高丽尽忠哉。先祖与文忠。其忠于高丽。终始同耳。直以殉节有早晚之异。而见者不察。便有轻重于其间。向亦闻左右以为此特一谏臣事耳。不足以当盛美。夫忧国之将亡而谏以至于死。此与逄,干岂有优劣。逄,干又何可少哉。而顾欲以近似未当之辞而为阐明之义哉。高丽之亡。殉于社稷者。二人而已。前者先祖而后者文忠。今日之欲发明先德。外此岂又有他义哉。前日书。曾亦略及此意。而其说不及尽。想未能细领。传神写影。尚恐一毛之有爽。况论其心之所存而可使有纤忽之差耶。属人与自为。惟雅意所欲。然若所以阐明主意。不容不审。幸加精思焉。见今世凡涉议论。为之极难出口。而此事关于先德。终不可以自默。故缕缕及此。必能深会。不以为罪也。答南云路书
原书曰。昨日泰辅来。更理别时十一之语。此于十一之数虽合。上农下农用力不同。而秋后收分。勤惰无异。未知此不为未安耶。公田则虽藉众力之助。至其私田。粪治耕耘。各尽其力。各食其功可也。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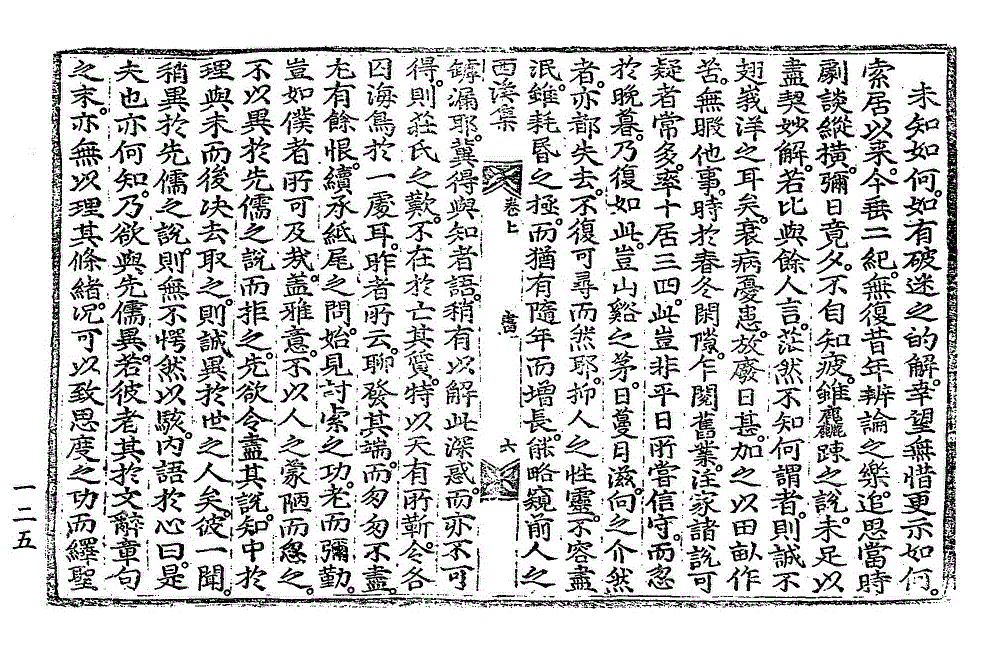 未知如何。如有破迷之的解。幸望无惜更示如何。
未知如何。如有破迷之的解。幸望无惜更示如何。索居以来。今垂二纪。无复昔年辨论之乐。追思当时剧谈纵横。弥日竟夕。不自知疲。虽粗疏之说。未足以尽契妙解。若比与馀人言。茫然不知何谓者。则诚不翅峨洋之耳矣。衰病忧患。放废日甚。加之以田亩作苦。无暇他事。时于春冬闲隙。乍阅旧业。注家诸说可疑者常多。率十居三四。此岂非平日所尝信守。而忽于晚暮。乃复如此。岂山溪之茅。日蔓日滋。向之介然者。亦都失去。不复可寻而然耶。抑人之性灵。不容尽泯。虽耗昏之极。而犹有随年而增长。能略窥前人之罅漏耶。冀得与知者语。稍有以解此深惑。而亦不可得。则庄氏之叹。不在于亡其质。特以天有所靳。令各囚海鸟于一处耳。昨者所云。聊发其端。而悤悤不尽。尤有馀恨。续承纸尾之问。始见讨索之功。老而弥勤。岂如仆者所可及哉。盖雅意。不以人之蒙陋而忽之。不以异于先儒之说而拒之。先欲令尽其说。知中于理与未而后决去取之。则诚异于世之人矣。彼一闻稍异于先儒之说。则无不愕然以骇。内语于心曰。是夫也亦何知。乃欲与先儒异。若彼者其于文辞章句之末。亦无以理其条绪。况可以致思度之功而绎圣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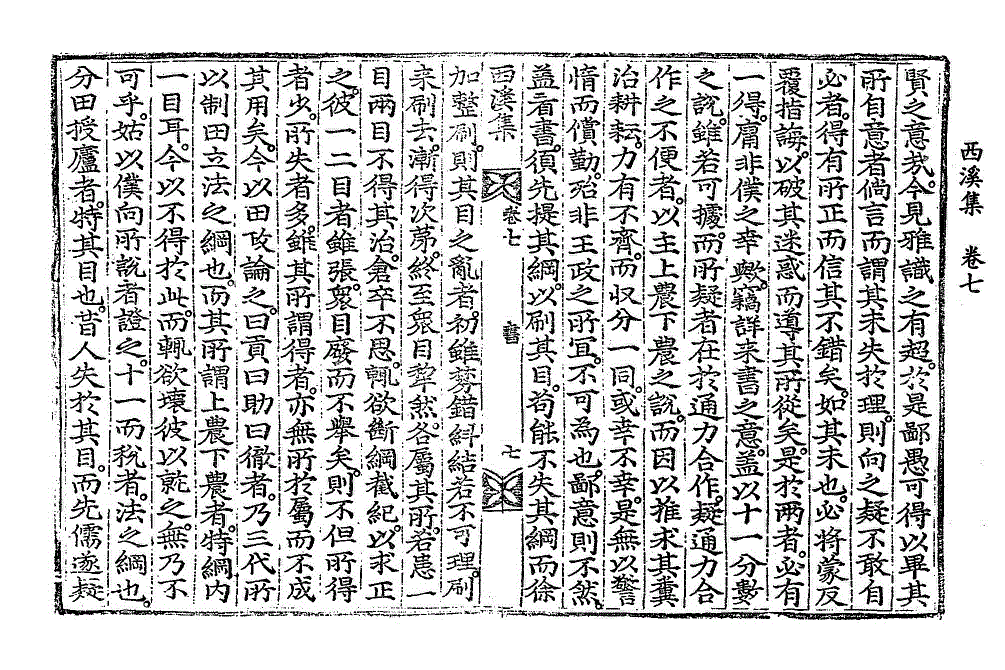 贤之意哉。今见雅识之有超于是。鄙愚可得以毕其所自意者。倘言而谓其未失于理。则向之疑不敢自必者。得有所正而信其不错矣。如其未也。必将蒙反覆指诲。以破其迷惑而导其所从矣。是于两者。必有一得。庸非仆之幸欤。窃详来书之意。盖以十一分数之说。虽若可据。而所疑者在于通力合作。疑通力合作之不便者。以主上农下农之说。而因以推求其粪治耕耘。力有不齐。而收分一同。或幸不幸。是无以警惰而偿勤。殆非王政之所宜。不可为也。鄙意则不然。盖看书。须先提其纲。以刷其目。苟能不失其纲而徐加整刷。则其目之乱者。初虽棼错纠结若不可理。刷来刷去。渐得次第。终至众目犁然。各属其所。若患一目两目不得其治。仓卒不思。辄欲断纲截纪。以求正之。彼一二目者虽张。众目发而不举矣。则不但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虽其所谓得者。亦无所于属而不成其用矣。今以田政论之。曰贡曰助曰彻者。乃三代所以制田立法之纲也。而其所谓上农下农者。特纲内一目耳。今以不得于此。而辄欲坏彼以就之。无乃不可乎。姑以仆向所说者證之。十一而税者。法之纲也。分田授庐者。特其目也。昔人失于其目。而先儒遂疑
贤之意哉。今见雅识之有超于是。鄙愚可得以毕其所自意者。倘言而谓其未失于理。则向之疑不敢自必者。得有所正而信其不错矣。如其未也。必将蒙反覆指诲。以破其迷惑而导其所从矣。是于两者。必有一得。庸非仆之幸欤。窃详来书之意。盖以十一分数之说。虽若可据。而所疑者在于通力合作。疑通力合作之不便者。以主上农下农之说。而因以推求其粪治耕耘。力有不齐。而收分一同。或幸不幸。是无以警惰而偿勤。殆非王政之所宜。不可为也。鄙意则不然。盖看书。须先提其纲。以刷其目。苟能不失其纲而徐加整刷。则其目之乱者。初虽棼错纠结若不可理。刷来刷去。渐得次第。终至众目犁然。各属其所。若患一目两目不得其治。仓卒不思。辄欲断纲截纪。以求正之。彼一二目者虽张。众目发而不举矣。则不但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虽其所谓得者。亦无所于属而不成其用矣。今以田政论之。曰贡曰助曰彻者。乃三代所以制田立法之纲也。而其所谓上农下农者。特纲内一目耳。今以不得于此。而辄欲坏彼以就之。无乃不可乎。姑以仆向所说者證之。十一而税者。法之纲也。分田授庐者。特其目也。昔人失于其目。而先儒遂疑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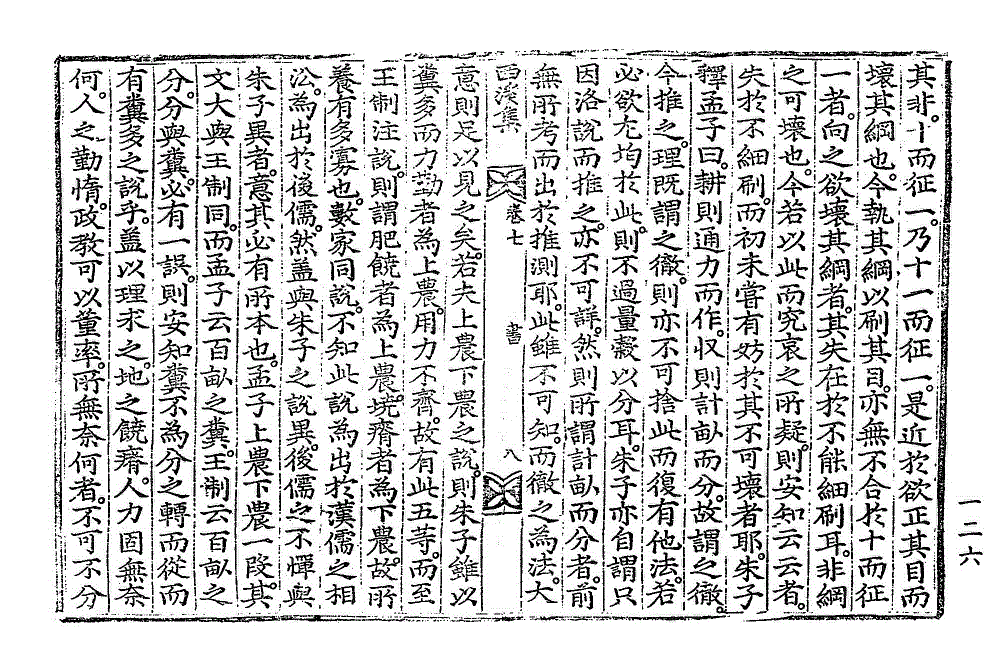 其非。十而征一。乃十一而征一。是近于欲正其目而坏其纲也。今执其纲以刷其目。亦无不合于十而征一者。向之欲坏其纲者。其失在于不能细刷耳。非纲之可坏也。今若以此而究哀之所疑。则安知云云者失于不细刷。而初未尝有妨于其不可坏者耶。朱子释孟子曰。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今推之理。既谓之彻。则亦不可舍此而复有他法。若必欲尤均于此。则不过量谷以分耳。朱子亦自谓只因洛说而推之。亦不可详。然则所谓计亩而分者。前无所考而出于推测耶。此虽不可知。而彻之为法。大意则足以见之矣。若夫上农下农之说。则朱子虽以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用力不齐。故有此五等。而至王制注说。则谓肥饶者为上农。硗瘠者为下农。故所养有多寡也。数家同说。不知此说为出于汉儒之相沿。为出于后儒。然盖与朱子之说异。后儒之不惮与朱子异者。意其必有所本也。孟子上农下农一段。其文大与王制同。而孟子云百亩之粪。王制云百亩之分。分与粪。必有一误。则安知粪不为分之转而从而有粪多之说乎。盖以理求之。地之饶瘠。人力固无奈何。人之勤惰。政教可以董率。所无奈何者。不可不分
其非。十而征一。乃十一而征一。是近于欲正其目而坏其纲也。今执其纲以刷其目。亦无不合于十而征一者。向之欲坏其纲者。其失在于不能细刷耳。非纲之可坏也。今若以此而究哀之所疑。则安知云云者失于不细刷。而初未尝有妨于其不可坏者耶。朱子释孟子曰。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今推之理。既谓之彻。则亦不可舍此而复有他法。若必欲尤均于此。则不过量谷以分耳。朱子亦自谓只因洛说而推之。亦不可详。然则所谓计亩而分者。前无所考而出于推测耶。此虽不可知。而彻之为法。大意则足以见之矣。若夫上农下农之说。则朱子虽以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用力不齐。故有此五等。而至王制注说。则谓肥饶者为上农。硗瘠者为下农。故所养有多寡也。数家同说。不知此说为出于汉儒之相沿。为出于后儒。然盖与朱子之说异。后儒之不惮与朱子异者。意其必有所本也。孟子上农下农一段。其文大与王制同。而孟子云百亩之粪。王制云百亩之分。分与粪。必有一误。则安知粪不为分之转而从而有粪多之说乎。盖以理求之。地之饶瘠。人力固无奈何。人之勤惰。政教可以董率。所无奈何者。不可不分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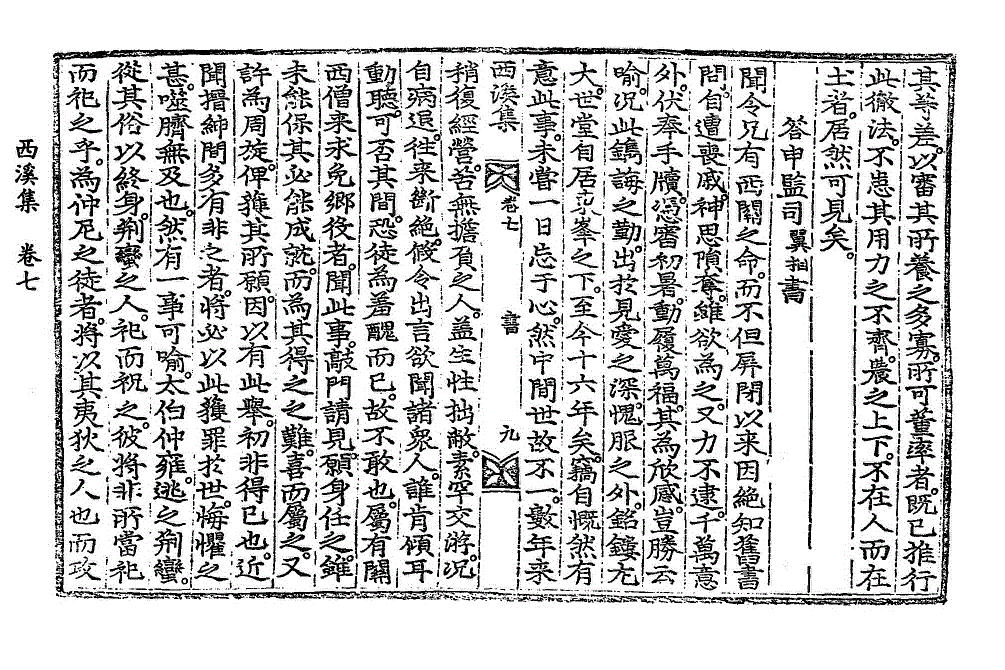 其等差。以审其所养之多寡。所可董率者。既已推行此彻法。不患其用力之不齐。农之上下。不在人而在土者。居然可见矣。
其等差。以审其所养之多寡。所可董率者。既已推行此彻法。不患其用力之不齐。农之上下。不在人而在土者。居然可见矣。答申监司(翼相)书
闻令兄有西关之命。而不但屏闭以来因绝知旧书问。自遭丧戚。神思陨夺。虽欲为之。又力不逮。千万意外。伏奉手牍。凭审初暑。动履万福。其为欣感。岂胜云喻。况此镌诲之勤。出于见爱之深。愧服之外。铭镂尤大。世堂自居东峰之下。至今十六年矣。窃自慨然有意此事。未尝一日忘于心。然中间世故不一。数年来稍复经营。苦无担负之人。盖生性拙敝。素罕交游。况自病退。往来断绝。假令出言欲闻诸众人。谁肯倾耳动听。可否其间。恐徒为羞丑而已。故不敢也。属有关西僧来求免乡役者。闻此事。敲门请见。愿身任之。虽未能保其必能成就。而为其得之之难。喜而属之。又许为周旋。俾获其所愿。因以有此举。初非得已也。近闻搢绅间多有非之者。将必以此获罪于世。悔惧之甚。噬脐无及也。然有一事可喻。太伯仲雍。逃之荆蛮。从其俗以终身。荆蛮之人。祀而祝之。彼将非所当祀而祀之乎。为仲尼之徒者。将以其夷狄之人也而攻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7L 页
 之。不诈其尚德之义。攘取而自祀之乎。抑其不然。见而叹之曰。德之感人。无分于夷夏如此。足见天理未泯之实。因奖与其善而助成之乎。明者必有以辨之矣。今此之事。亦何以异彼。而乃谓夫缁流之不得有所奉也。此愚鄙之所深惑也。不然。使今之闻者。奋然相告于众曰。此老之迹。不可使终泯于此山也久矣。吾辈莫有为者。而缁流为之。是吾辈之耻也。鸠财合力。以先其事。又谁曰不可。若其未也。而只斥缁流而已。则是闭人为善之门。非辟异端之谓也。仲尼曰。不念旧恶。曰与其进也。孟子言来者不拒。后儒亦有在夷狄则进之之说。圣贤待人之厚而与人为善之意。本自如此。何尝如今人迫隘褊狭。视若怨敌之为也。若如此纷纭。终至败坏其事。即无异于自不能奉其先生长者。而怒邻人之悯而收之。骂詈驱逐。使不得容。先生长者。既不得于彼。又不得于此。顾养无所。不已病矣。愿令兄深察愚意。去就此两端。若犹雅意之未改。亟谂于众。无使贻羞于邻人之养。倘以奖善。是亦一道。则广谕知识。同赐补助。俾卒有成。实非细幸也。
之。不诈其尚德之义。攘取而自祀之乎。抑其不然。见而叹之曰。德之感人。无分于夷夏如此。足见天理未泯之实。因奖与其善而助成之乎。明者必有以辨之矣。今此之事。亦何以异彼。而乃谓夫缁流之不得有所奉也。此愚鄙之所深惑也。不然。使今之闻者。奋然相告于众曰。此老之迹。不可使终泯于此山也久矣。吾辈莫有为者。而缁流为之。是吾辈之耻也。鸠财合力。以先其事。又谁曰不可。若其未也。而只斥缁流而已。则是闭人为善之门。非辟异端之谓也。仲尼曰。不念旧恶。曰与其进也。孟子言来者不拒。后儒亦有在夷狄则进之之说。圣贤待人之厚而与人为善之意。本自如此。何尝如今人迫隘褊狭。视若怨敌之为也。若如此纷纭。终至败坏其事。即无异于自不能奉其先生长者。而怒邻人之悯而收之。骂詈驱逐。使不得容。先生长者。既不得于彼。又不得于此。顾养无所。不已病矣。愿令兄深察愚意。去就此两端。若犹雅意之未改。亟谂于众。无使贻羞于邻人之养。倘以奖善。是亦一道。则广谕知识。同赐补助。俾卒有成。实非细幸也。与南相国(九万)书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8H 页
 暑炎比酷。伏惟台体万福。向承祈免。旋闻造朝。 天眷隆重。固难坚守。惟愿日进嘉猷。勉尽大臣之节。无徒以进退一节为自洁而已。观古人。进有一事。退有一事。不如近代名公其在位无可称。其去位无可名耳。世堂获蒙盛赐。粗保病骸。有私悰之迫。辄敢布露。先祖先亲。在于法例。俱当蒙易名之恩。而阅历四五十年。迄今不得。皆缘世堂等不肖。不早祈请。诸兄先后丧亡。世堂又死期不远。恐一朝溘然。为不瞑之恨。适幸家侄忝授藩任。光侈宠命。冀可得力。遂欲援例请恩。毋失此会。须求徵信之文。俾太常得有按据。而幸先德不至泯蔽。先祖行实之论摭。已获诺于太学士。惟是先亲立朝行己之迹。其阐发之托。舍执事而无所归。故为干渎。伏惟台兄必不以为不可。惟幸力为发挥。以为生死之荣。不胜祝祷。不胜祝祷。事宜躬请。负病替书。万万知罪。幸少亮恕。
暑炎比酷。伏惟台体万福。向承祈免。旋闻造朝。 天眷隆重。固难坚守。惟愿日进嘉猷。勉尽大臣之节。无徒以进退一节为自洁而已。观古人。进有一事。退有一事。不如近代名公其在位无可称。其去位无可名耳。世堂获蒙盛赐。粗保病骸。有私悰之迫。辄敢布露。先祖先亲。在于法例。俱当蒙易名之恩。而阅历四五十年。迄今不得。皆缘世堂等不肖。不早祈请。诸兄先后丧亡。世堂又死期不远。恐一朝溘然。为不瞑之恨。适幸家侄忝授藩任。光侈宠命。冀可得力。遂欲援例请恩。毋失此会。须求徵信之文。俾太常得有按据。而幸先德不至泯蔽。先祖行实之论摭。已获诺于太学士。惟是先亲立朝行己之迹。其阐发之托。舍执事而无所归。故为干渎。伏惟台兄必不以为不可。惟幸力为发挥。以为生死之荣。不胜祝祷。不胜祝祷。事宜躬请。负病替书。万万知罪。幸少亮恕。答尹子仁书
别纸所教。有以见垂哀俯矜勤至之盛意。敢不佩服。至此无忘仁者之赐。顾此愚蔽。尚有一二未能洞然无疑于来谕者。则亦不敢直谓老兄未契鄙陋所云。不可与强聒而终闭不见。以自隳区区相信之诚。辄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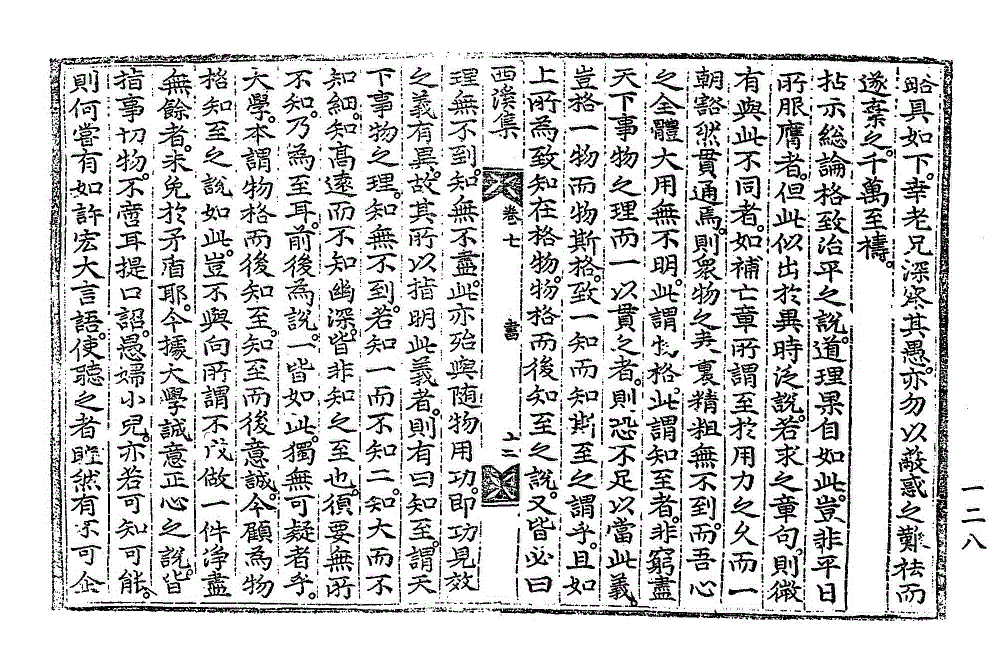 略具如下。幸老兄深察其愚。亦勿以蔽惑之难祛而遂弃之。千万至祷。
略具如下。幸老兄深察其愚。亦勿以蔽惑之难祛而遂弃之。千万至祷。拈示总论格致治平之说。道理果自如此。岂非平日所服膺者。但此似出于异时泛说。若求之章句。则微有与此不同者。如补亡章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朝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此谓物格。此谓知至者。非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而一以贯之者。则恐不足以当此义。岂格一物而物斯格。致一知而知斯至之谓乎。且如上所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说。又皆必曰理无不到。知无不尽。此亦殆与随物用功。即功见效之义有异。故其所以指明此义者。则有曰知至。谓天下事物之理。知无不到。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细。知高远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须要无所不知。乃为至耳。前后为说。一皆如此。独无可疑者乎。大学。本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今顾为物格知至之说如此。岂不与向所谓不成做一件净尽无馀者。未免于矛盾耶。今据大学诚意正心之说。皆指事切物。不啻耳提口诏。愚妇小儿。亦若可知可能。则何尝有如许宏大言语。使听之者瞠然有不可企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9H 页
 及之忧耶。此愚陋之所甚惑。不审老兄于此。信以为不然乎。若是则愚陋所疑。不在传文而在于章句。所谓知彻。非众物之理无不到之谓。只言一物而馀可推见也。
及之忧耶。此愚陋之所甚惑。不审老兄于此。信以为不然乎。若是则愚陋所疑。不在传文而在于章句。所谓知彻。非众物之理无不到之谓。只言一物而馀可推见也。井有仁一章。文义本自浅易。不难见也。常谓先儒偶失于此。今老兄坚守至此。窃不胜怃然。此章之指。不在于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乎。老兄且试掉下仁字勿论。只把告之曰井有人一句。反覆致详。见此所告。本非理之所无。而其告之者。未觉其辄有相陷之端。则即可悟人字之误而旧文为正也。盖欲从仁而入井。是为见陷。而君子不然。故曰不可陷也。信仁之在井。是为见罔。而君子不然。故曰不可罔也。今求之于所谓井有人者。则终未见其为陷为罔。圣人何故辄谓不可陷不可罔也。只如来谕人落井中故往见者。正见其非陷非罔。而若谓仁在井中。孰有往见者。又明其为不可陷不可罔也。而乃反以此为见攻之说。真所谓弟子之惑滋甚者也。盖夫子所言可逝不丁陷。以答宰我其从之一句。可欺不可罔。以答宰我所设井有仁一句。意各有所指。非如今老兄所云也。上两段所论。皆为虽蒙指诲之缕缕。而愚蔽犹前。更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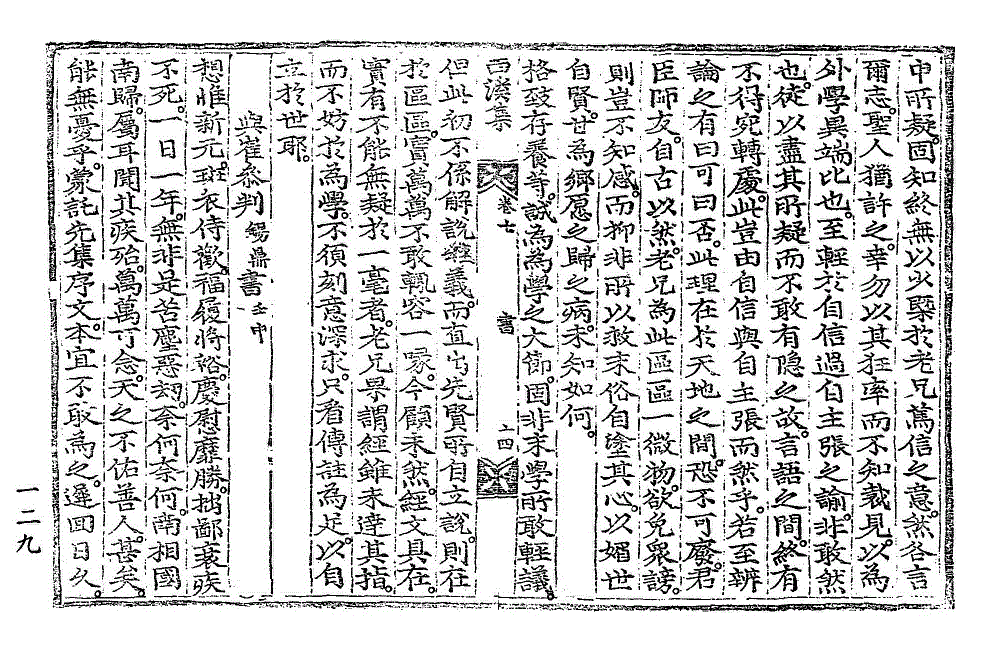 申所疑。固知终无以少槩于老兄笃信之意。然各言尔志。圣人犹许之。幸勿以其狂率而不知裁见。以为外学异端比也。至轻于自信过自主张之谕。非敢然也。徒以尽其所疑而不敢有隐之。故言语之间。终有不得宛转处。此岂由自信与自主张而然乎。若至辨论之有曰可曰否。此理在于天地之间。恐不可废。君臣师友。自古以然。老兄为此区区一微物。欲免众谤。则岂不知感。而抑非所以救末俗。自涂其心。以媚世自贤。甘为乡愿之归之病。未知如何。
申所疑。固知终无以少槩于老兄笃信之意。然各言尔志。圣人犹许之。幸勿以其狂率而不知裁见。以为外学异端比也。至轻于自信过自主张之谕。非敢然也。徒以尽其所疑而不敢有隐之。故言语之间。终有不得宛转处。此岂由自信与自主张而然乎。若至辨论之有曰可曰否。此理在于天地之间。恐不可废。君臣师友。自古以然。老兄为此区区一微物。欲免众谤。则岂不知感。而抑非所以救末俗。自涂其心。以媚世自贤。甘为乡愿之归之病。未知如何。格致存养等。诚为为学之大节。固非末学所敢轻议。但此初不系解说经义。而直出先贤所自立说。则在于区区。宾万万不敢辄容一喙。今顾未然。经文具在。实有不能无疑于一毫者。老兄果谓经虽未达其指。而不妨于为学。不须刻意深求。只看传注。为足以自立于世耶。
与崔参判(锡鼎)书(壬申)
想惟新元。斑衣侍欢。福履将裕。庆慰靡胜。拙鄙衰疾不死。一日一年。无非是苦尘恶劫。奈何奈何。南相国南归。属耳闻其疾殆。万万可念。天之不佑善人。甚矣。能无忧乎。蒙托先集序文。本宜不敢为之。迟回日久。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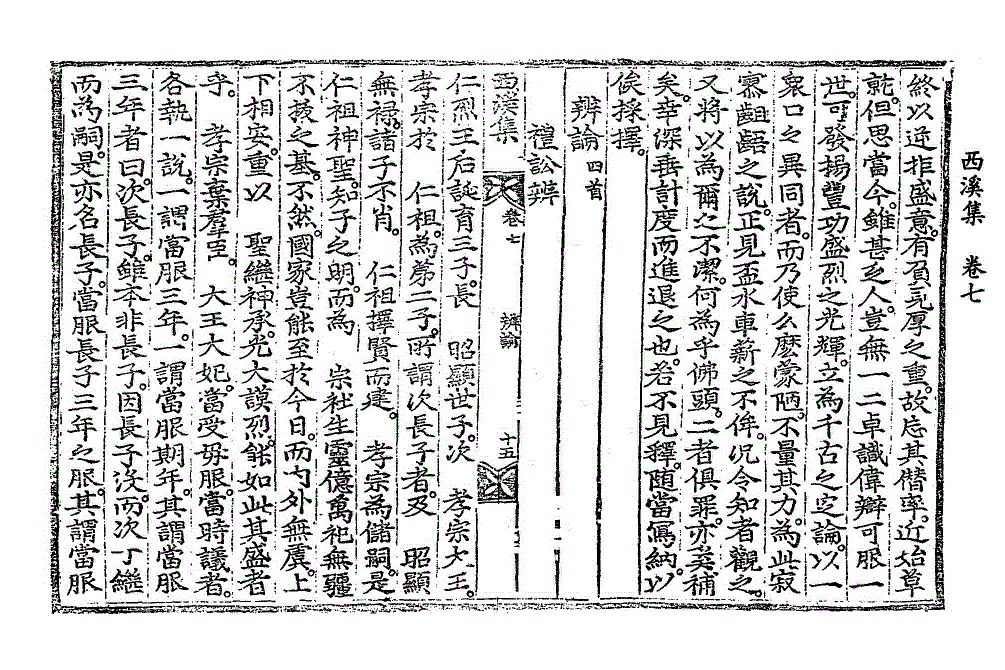 终以逆拒盛意。有负见厚之重。故忘其僭率。近始草就。但思当今。虽甚乏人。岂无一二卓识伟辨可服一世。可发扬丰功盛烈之光辉。立为千古之定论。以一众口之异同者。而乃使幺么蒙陋。不量其力。为此寂寥龃龉之说。正见杯水车薪之不侔。况令知者观之。又将以为尔之不洁。何为乎佛头。二者俱罪。亦奚补矣。幸深垂计度而进退之也。若不见释。随当写纳。以俟采择。
终以逆拒盛意。有负见厚之重。故忘其僭率。近始草就。但思当今。虽甚乏人。岂无一二卓识伟辨可服一世。可发扬丰功盛烈之光辉。立为千古之定论。以一众口之异同者。而乃使幺么蒙陋。不量其力。为此寂寥龃龉之说。正见杯水车薪之不侔。况令知者观之。又将以为尔之不洁。何为乎佛头。二者俱罪。亦奚补矣。幸深垂计度而进退之也。若不见释。随当写纳。以俟采择。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辨论(四首)
礼讼辨
仁烈王后诞育三子。长 昭显世子。次 孝宗大王。孝宗于 仁祖。为弟二子。所谓次长子者。及 昭显无禄。诸子不肖。 仁祖择贤。而建 孝宗为储嗣。是仁祖神圣知子之明。而为 宗社生灵亿万祀无疆不拔之基。不然。国家岂能至于今日。而内外无虞。上下相安。重以 圣继神承。光大谟烈。能如此其盛者乎。 孝宗弃群臣。 大王大妃。当受母服。当时议者。各执一说。一谓当服三年。一谓当服期年。其谓当服三年者曰。次长子。虽本非长子。因长子没。而次子继而为嗣。是亦名长子。当服长子三年之服。其谓当服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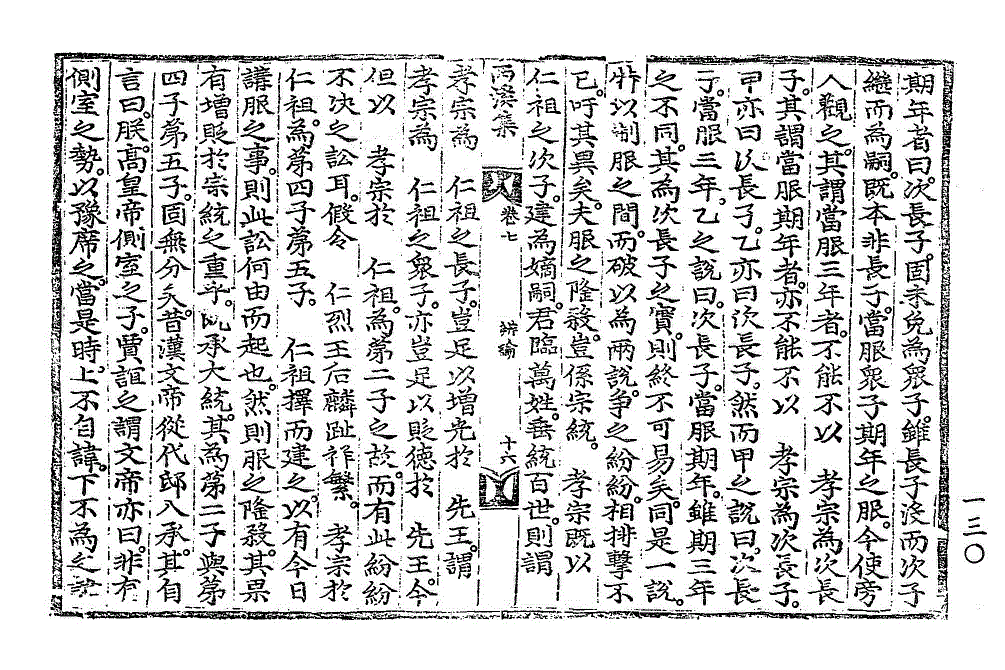 期年者曰。次长子。固未免为众子。虽长子没而次子继而为嗣。既本非长子。当服众子期年之服。今使旁人观之。其谓当服三年者。不能不以 孝宗为次长子。其谓当服期年者。亦不能不以 孝宗为次长子。甲亦曰次长子。乙亦曰次长子。然而甲之说曰。次长子。当服三年。乙之说曰。次长子。当服期年。虽期三年之不同。其为次长子之实。则终不可易矣。同是一说。特以制服之间。而破以为两说。争之纷纷。相排击不已。吁其异矣。夫服之隆杀。岂系宗统。 孝宗既以 仁祖之次子。建为嫡嗣。君临万姓。垂统百世。则谓 孝宗为 仁祖之长子。岂足以增光于 先王。谓 孝宗为 仁祖之众子。亦岂足以贬德于 先王。今但以 孝宗于 仁祖。为第二子之故。而有此纷纷不决之讼耳。假令 仁烈王后麟趾祥繁。 孝宗于仁祖。为第四子第五子。 仁祖择而建之。以有今日讲服之事。则此讼何由而起也。然则服之隆杀。其果有增贬于宗统之重乎。既承大统。其为第二子与弟四子第五子。固无分矣。昔汉文帝从代邸入承。其自言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贾谊之谓文帝亦曰。非有侧室之势以豫席之。当是时。上不自讳。下不为之讳
期年者曰。次长子。固未免为众子。虽长子没而次子继而为嗣。既本非长子。当服众子期年之服。今使旁人观之。其谓当服三年者。不能不以 孝宗为次长子。其谓当服期年者。亦不能不以 孝宗为次长子。甲亦曰次长子。乙亦曰次长子。然而甲之说曰。次长子。当服三年。乙之说曰。次长子。当服期年。虽期三年之不同。其为次长子之实。则终不可易矣。同是一说。特以制服之间。而破以为两说。争之纷纷。相排击不已。吁其异矣。夫服之隆杀。岂系宗统。 孝宗既以 仁祖之次子。建为嫡嗣。君临万姓。垂统百世。则谓 孝宗为 仁祖之长子。岂足以增光于 先王。谓 孝宗为 仁祖之众子。亦岂足以贬德于 先王。今但以 孝宗于 仁祖。为第二子之故。而有此纷纷不决之讼耳。假令 仁烈王后麟趾祥繁。 孝宗于仁祖。为第四子第五子。 仁祖择而建之。以有今日讲服之事。则此讼何由而起也。然则服之隆杀。其果有增贬于宗统之重乎。既承大统。其为第二子与弟四子第五子。固无分矣。昔汉文帝从代邸入承。其自言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贾谊之谓文帝亦曰。非有侧室之势以豫席之。当是时。上不自讳。下不为之讳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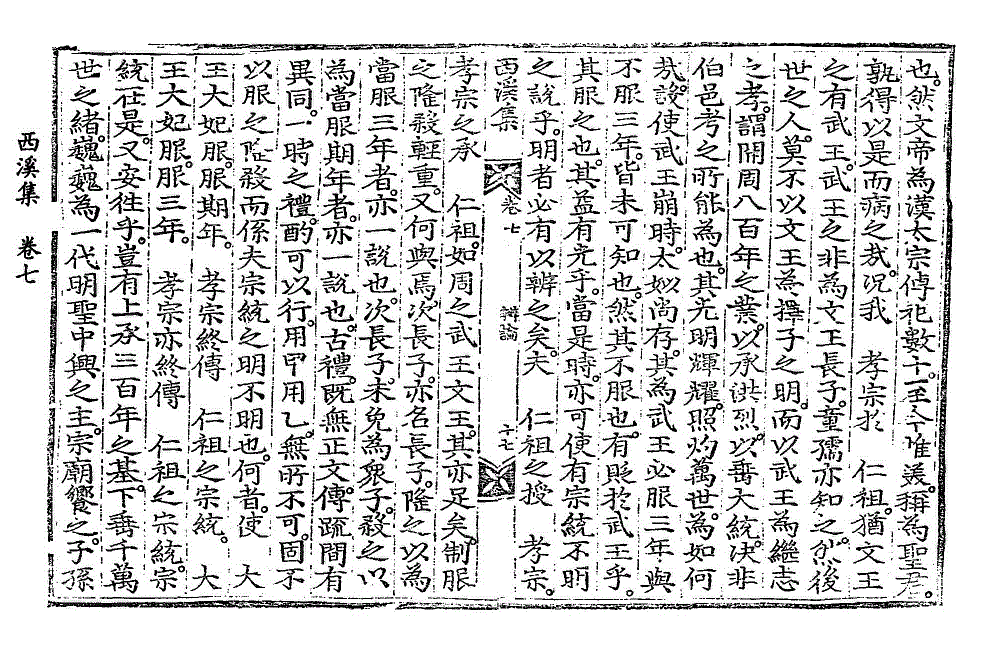 也。然文帝为汉太宗传祀数十。至今唯美。称为圣君。孰得以是而病之哉。况我 孝宗于 仁祖。犹文王之有武王。武王之非为文王长子。童孺亦知之。然后世之人。莫不以文王为择子之明。而以武王为继志之孝。谓开周八百年之业。以承洪烈。以垂大统。决非伯邑考之所能为也。其光明辉耀。照灼万世。为如何哉。设使武王崩时。太姒尚存。其为武王必服三年与不服二年。皆未可知也。然其不服也。有贬于武王乎。其服之也。其益有光乎。当是时。亦可使有宗统不明之说乎。明者必有以辨之矣。夫 仁祖之授 孝宗。孝宗之承 仁祖。如周之武王文王。其亦足矣。制服之隆杀轻重。又何与焉。次长子。亦名长子。隆之以为当服三年者。亦一说也。次长子。未免为众子。杀之以为当服期年者。亦一说也。古礼。既无正文。传疏间有异同。一时之礼。酌可以行。用甲用乙。无所不可。固不以服之隆杀而系夫宗统之明不明也。何者。使 大王大妃服。服期年。 孝宗终传 仁祖之宗统。 大王大妃服。服三年。 孝宗亦终传 仁祖之宗统。宗统在是。又安往乎。岂有上承三百年之基。下垂千万世之绪。巍巍为一代明圣中兴之主。宗庙飨之。子孙
也。然文帝为汉太宗传祀数十。至今唯美。称为圣君。孰得以是而病之哉。况我 孝宗于 仁祖。犹文王之有武王。武王之非为文王长子。童孺亦知之。然后世之人。莫不以文王为择子之明。而以武王为继志之孝。谓开周八百年之业。以承洪烈。以垂大统。决非伯邑考之所能为也。其光明辉耀。照灼万世。为如何哉。设使武王崩时。太姒尚存。其为武王必服三年与不服二年。皆未可知也。然其不服也。有贬于武王乎。其服之也。其益有光乎。当是时。亦可使有宗统不明之说乎。明者必有以辨之矣。夫 仁祖之授 孝宗。孝宗之承 仁祖。如周之武王文王。其亦足矣。制服之隆杀轻重。又何与焉。次长子。亦名长子。隆之以为当服三年者。亦一说也。次长子。未免为众子。杀之以为当服期年者。亦一说也。古礼。既无正文。传疏间有异同。一时之礼。酌可以行。用甲用乙。无所不可。固不以服之隆杀而系夫宗统之明不明也。何者。使 大王大妃服。服期年。 孝宗终传 仁祖之宗统。 大王大妃服。服三年。 孝宗亦终传 仁祖之宗统。宗统在是。又安往乎。岂有上承三百年之基。下垂千万世之绪。巍巍为一代明圣中兴之主。宗庙飨之。子孙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1L 页
 保之。然犹且以服有隆杀而见谓宗统之不明者乎。然则今日之因争典礼而执为宗统不明之说者。其亦不仁甚矣。其亦欲有所激而故假之说矣。其亦欲有所挤而故借之名矣。其为心也。吁亦险且危哉。
保之。然犹且以服有隆杀而见谓宗统之不明者乎。然则今日之因争典礼而执为宗统不明之说者。其亦不仁甚矣。其亦欲有所激而故假之说矣。其亦欲有所挤而故借之名矣。其为心也。吁亦险且危哉。辨和叔论纪年示儿侄
和叔论立石年月。大段舛误。其所云洪范之义者。先儒之说。荡无经据。孔氏以泰誓言年。洪范言祀。未得其说。妄以意傅会。厥后诸儒遂因而守之。不察事理之反戾不成。今乃援此以为證。又何知所證之不足凭乎。夫书之称十有三祀者。其义有不可详。或是武王改商之初。年祀之名。未有所易。及后整顿。以新一王之制。而当时史官记事也。有追正也。有未及正。所以彼此之不同。亦未可知。但此明非箕子之所自言。而孔氏乃曰。箕子称祀不忘本。只此已见其妄。及后儒守其说而亦觉其有少未安。则又迁就而敷演之。以为史官因箕子之辞。夫上下宾主之相见。古今岂异。安有先讲年祀之名。岁数之几何。以为礼者乎。若又以为此史官之追记。而以箕子不忘商不臣周。平日私所自识时月者如此。故因其辞耳。非箕子见武王之时有讲年祀之事云尔。则愈不掩其辞之遁也。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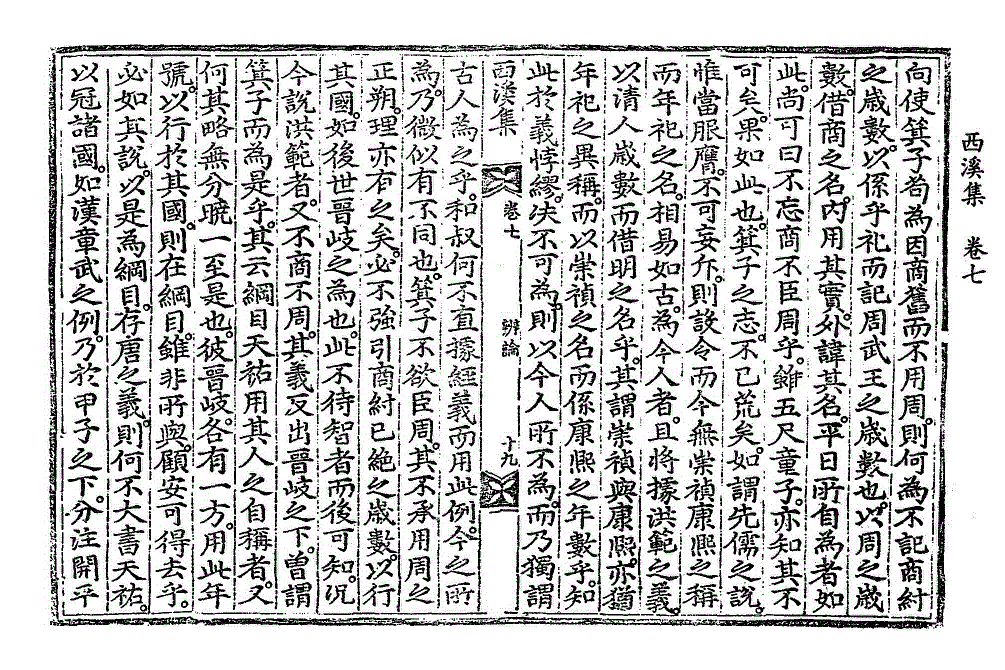 向使箕子苟为因商旧而不用周。则何为不记商纣之岁数。以系乎祀而记周武王之岁数也。以周之岁数。借商之名。内用其实。外讳其名。平日所自为者如此。尚可曰不忘商不臣周乎。虽五尺章子。亦知其不可矣。果如此也。箕子之志。不已荒矣。如谓先儒之说。惟当服膺。不可妄斥。则设令而今无崇祯康熙之称而年祀之名。相易如古。为今人者。且将据洪范之义。以清人岁数而借明之名乎。其谓崇祯与康熙。亦犹年祀之异称。而以崇祯之名而系康熙之年数乎。知此于义悖缪。决不可为。则以今人所不为。而乃独谓古人为之乎。和叔何不直据经义而用此例。今之所为。乃微似有不同也。箕子不欲臣周。其不承用周之正朔。理亦有之矣。必不强引商纣已绝之岁数。以行其国。如后世晋岐之为也。此不待智者而后可知。况今说洪范者。又不商不周。其义反出晋岐之下。曾谓箕子而为是乎。其云纲目天祐用其人之自称者。又何其略无分晓一至是也。彼晋岐。各有一方。用此年号。以行于其国。则在纲目。虽非所与。顾安可得去乎。必如其说。以是为纲目存唐之义。则何不大书天祐。以冠诸国。如汉章武之例。乃于甲子之下。分注开平
向使箕子苟为因商旧而不用周。则何为不记商纣之岁数。以系乎祀而记周武王之岁数也。以周之岁数。借商之名。内用其实。外讳其名。平日所自为者如此。尚可曰不忘商不臣周乎。虽五尺章子。亦知其不可矣。果如此也。箕子之志。不已荒矣。如谓先儒之说。惟当服膺。不可妄斥。则设令而今无崇祯康熙之称而年祀之名。相易如古。为今人者。且将据洪范之义。以清人岁数而借明之名乎。其谓崇祯与康熙。亦犹年祀之异称。而以崇祯之名而系康熙之年数乎。知此于义悖缪。决不可为。则以今人所不为。而乃独谓古人为之乎。和叔何不直据经义而用此例。今之所为。乃微似有不同也。箕子不欲臣周。其不承用周之正朔。理亦有之矣。必不强引商纣已绝之岁数。以行其国。如后世晋岐之为也。此不待智者而后可知。况今说洪范者。又不商不周。其义反出晋岐之下。曾谓箕子而为是乎。其云纲目天祐用其人之自称者。又何其略无分晓一至是也。彼晋岐。各有一方。用此年号。以行于其国。则在纲目。虽非所与。顾安可得去乎。必如其说。以是为纲目存唐之义。则何不大书天祐。以冠诸国。如汉章武之例。乃于甲子之下。分注开平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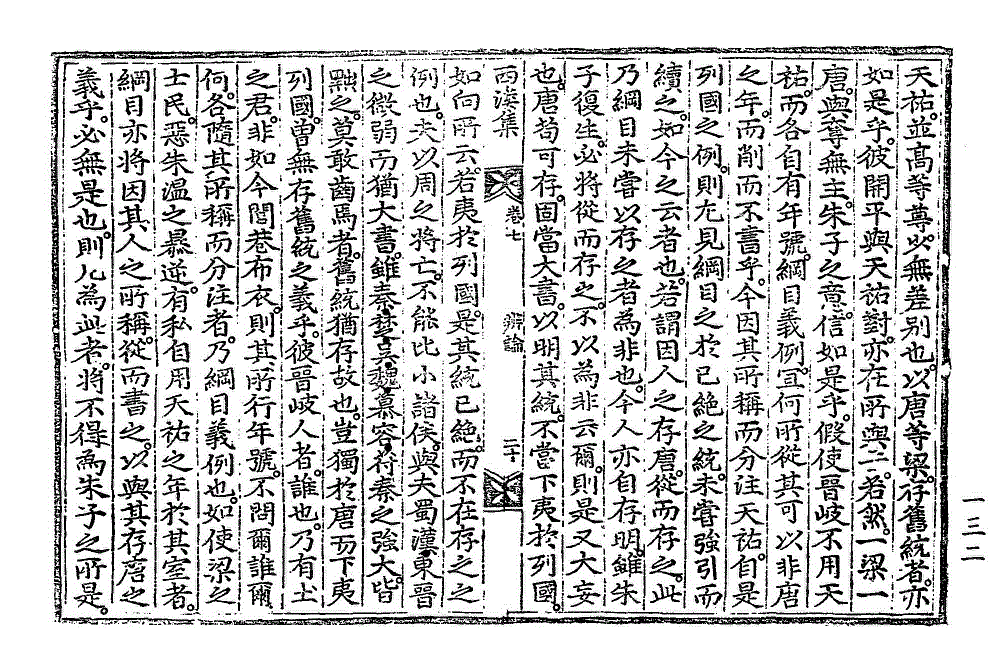 天祐。并高等尊。少无差别也。以唐等梁。存旧统者。亦如是乎。彼开平与天祐对。亦在所与乎。若然。一梁一唐。与夺无主。朱子之意。信如是乎。假使晋岐不用天祐。而各自有年号。纲目义例。宜何所从。其可以非唐之年。而削而不书乎。今因其所称而分注天祐。自是列国之例。则尤见纲目之于已绝之统。未尝强引而续之。如今之云者也。若谓因人之存唐。从而存之。此乃纲目未尝以存之者为非也。今人亦自存明。虽朱子复生。必将从而存之。不以为非云尔。则是又大妄也。唐苟可存。固当大书。以明其统。不当下夷于列国。如向所云。若夷于列国。是其统已绝。而不在存之之例也。夫以周之将亡。不能比小诸侯。与夫蜀汉,东晋之微弱而犹大书。虽秦,楚,吴,魏,慕容,苻秦之强大。皆黜之。莫敢齿焉者。旧统犹存故也。岂独于唐而下夷列国。曾无存旧统之义乎。彼晋岐人者。谁也。乃有土之君。非如今闾巷布衣。则其所行年号。不问尔谁尔何。各随其所称而分注者。乃纲目义例也。如使梁之士民。恶朱温之暴逆。有私自用天祐之年于其室者。纲目亦将因其人之所称。从而书之。以与其存唐之义乎。必无是也。则凡为此者。将不得为朱子之所是。
天祐。并高等尊。少无差别也。以唐等梁。存旧统者。亦如是乎。彼开平与天祐对。亦在所与乎。若然。一梁一唐。与夺无主。朱子之意。信如是乎。假使晋岐不用天祐。而各自有年号。纲目义例。宜何所从。其可以非唐之年。而削而不书乎。今因其所称而分注天祐。自是列国之例。则尤见纲目之于已绝之统。未尝强引而续之。如今之云者也。若谓因人之存唐。从而存之。此乃纲目未尝以存之者为非也。今人亦自存明。虽朱子复生。必将从而存之。不以为非云尔。则是又大妄也。唐苟可存。固当大书。以明其统。不当下夷于列国。如向所云。若夷于列国。是其统已绝。而不在存之之例也。夫以周之将亡。不能比小诸侯。与夫蜀汉,东晋之微弱而犹大书。虽秦,楚,吴,魏,慕容,苻秦之强大。皆黜之。莫敢齿焉者。旧统犹存故也。岂独于唐而下夷列国。曾无存旧统之义乎。彼晋岐人者。谁也。乃有土之君。非如今闾巷布衣。则其所行年号。不问尔谁尔何。各随其所称而分注者。乃纲目义例也。如使梁之士民。恶朱温之暴逆。有私自用天祐之年于其室者。纲目亦将因其人之所称。从而书之。以与其存唐之义乎。必无是也。则凡为此者。将不得为朱子之所是。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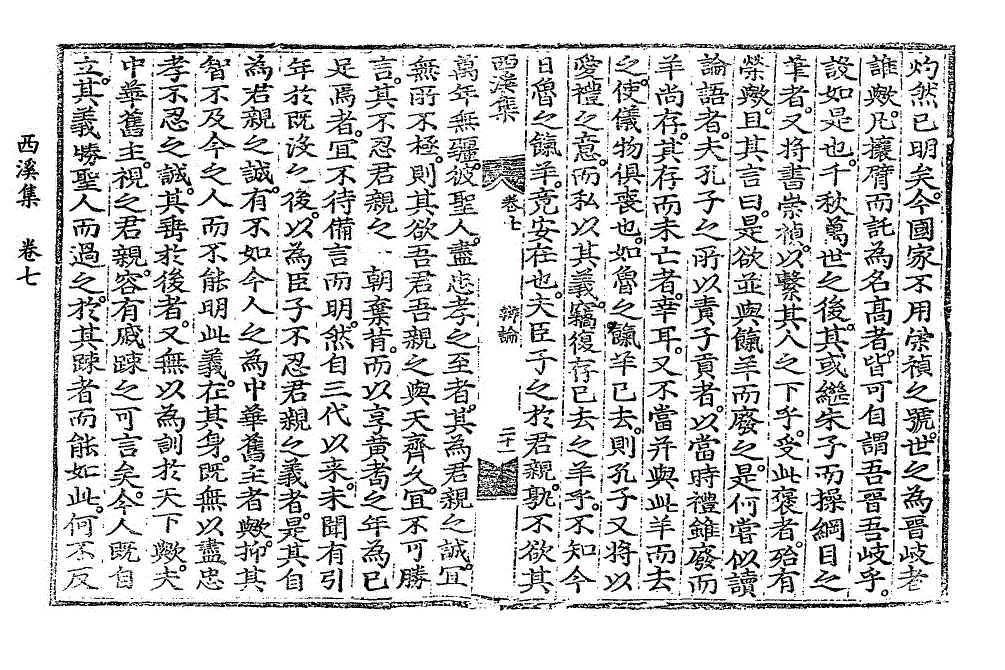 灼然已明矣。今国家不用崇祯之号。世之为晋岐者谁欤。凡攘臂而托为名高者。皆可自谓吾晋吾岐乎。设如是也。千秋万世之后。其或继朱子而操纲目之笔者。又将书崇祯。以系其人之下乎。受此褒者。殆有荣欤。且其言曰。是欲并与饩羊而废之。是何尝似读论语者。夫孔子之所以责子贡者。以当时礼虽废而羊尚存。其存而未亡者。幸耳。又不当并与此羊而去之。使仪物俱丧也。如鲁之饩羊已去。则孔子又将以爱礼之意。而私以其义。窃复存已去之羊乎。不知今日鲁之饩羊。竟安在也。夫臣子之于君亲。孰不欲其万年无疆。彼圣人尽忠孝之至者。其为君亲之诚。宜无所不极。则其欲吾君吾亲之与天齐久。宜不可胜言。其不忍君亲之一朝弃背。而以享黄耇之年为已足焉者。宜不待备言而明。然自三代以来。未闻有引年于既没之后。以为臣子不忍君亲之义者。是其自为君亲之诚。有不如今人之为中华旧主者欤。抑其智不及今之人而不能明此义。在其身既无以尽忠孝不忍之诚。其垂于后者又无以为训于天下欤。夫中华旧主。视之君亲。容有戚疏之可言矣。今人既自立其义。胜圣人而过之。于其疏者而能如此。何不反
灼然已明矣。今国家不用崇祯之号。世之为晋岐者谁欤。凡攘臂而托为名高者。皆可自谓吾晋吾岐乎。设如是也。千秋万世之后。其或继朱子而操纲目之笔者。又将书崇祯。以系其人之下乎。受此褒者。殆有荣欤。且其言曰。是欲并与饩羊而废之。是何尝似读论语者。夫孔子之所以责子贡者。以当时礼虽废而羊尚存。其存而未亡者。幸耳。又不当并与此羊而去之。使仪物俱丧也。如鲁之饩羊已去。则孔子又将以爱礼之意。而私以其义。窃复存已去之羊乎。不知今日鲁之饩羊。竟安在也。夫臣子之于君亲。孰不欲其万年无疆。彼圣人尽忠孝之至者。其为君亲之诚。宜无所不极。则其欲吾君吾亲之与天齐久。宜不可胜言。其不忍君亲之一朝弃背。而以享黄耇之年为已足焉者。宜不待备言而明。然自三代以来。未闻有引年于既没之后。以为臣子不忍君亲之义者。是其自为君亲之诚。有不如今人之为中华旧主者欤。抑其智不及今之人而不能明此义。在其身既无以尽忠孝不忍之诚。其垂于后者又无以为训于天下欤。夫中华旧主。视之君亲。容有戚疏之可言矣。今人既自立其义。胜圣人而过之。于其疏者而能如此。何不反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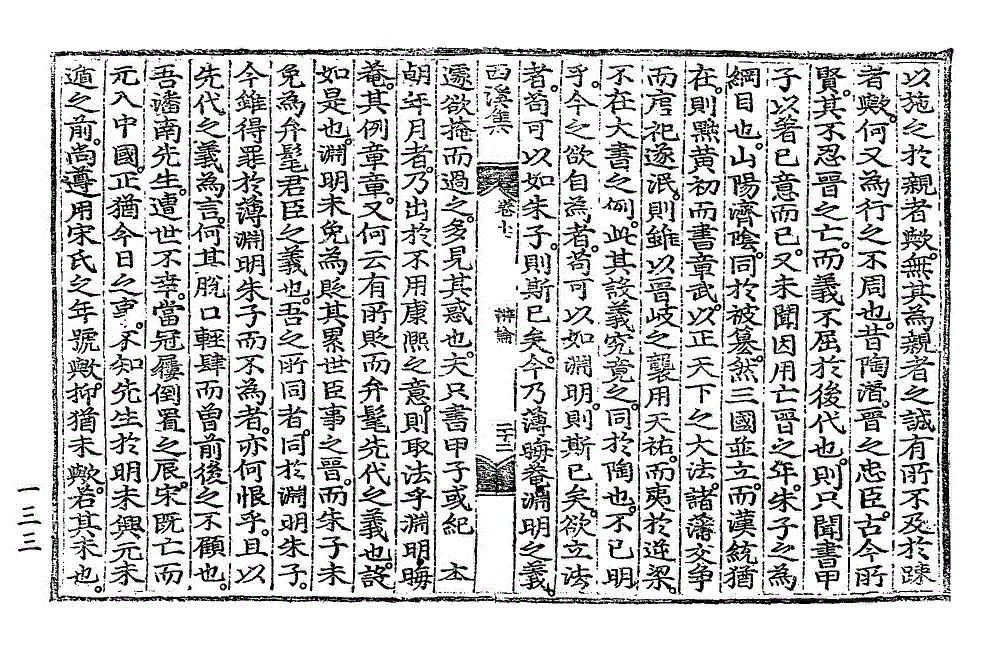 以施之于亲者欤。无其为亲者之诚有所不及于疏者欤。何又为行之不周也。昔陶潜。晋之忠臣。古今所贤。其不忍晋之亡。而义不屈于后代也。则只闻书甲子以著己意而已。又未闻因用亡晋之年。朱子之为纲目也。山阳济阴。同于被篡。然三国并立。而汉统犹在。则黜黄初而书章武。以正天下之大法。诸藩交争。而唐祀遂泯。则虽以晋岐之袭用天祜。而夷于逆梁。不在大书之例。此其设义究竟之同于陶也。不已明乎。今之欲自为者。苟可以如渊明。则斯已矣。欲立法者。苟可以如朱子。则斯已矣。今乃薄晦庵,渊明之义。遽欲掩而过之。多见其惑也。夫只书甲子或纪 本朝年月者。乃出于不用康熙之意。则取法乎渊明,晦庵。其例章章。又何云有所贬而弁髦先代之义也。设如是也。渊明未免为贬其累世臣事之晋。而朱子未免为弁髦君臣之义也。吾之所同者。同于渊明朱子。今虽得罪于薄渊明朱子而不为者。亦何恨乎。且以先代之义为言。何其脱口轻肆而曾前后之不顾也。吾潘南先生。遭世不幸。当冠屦倒置之辰。宋既亡而元入中国。正犹今日之事。不知先生于明未兴元未遁之前。尚遵用宋氏之年号欤。抑犹未欤。若其未也。
以施之于亲者欤。无其为亲者之诚有所不及于疏者欤。何又为行之不周也。昔陶潜。晋之忠臣。古今所贤。其不忍晋之亡。而义不屈于后代也。则只闻书甲子以著己意而已。又未闻因用亡晋之年。朱子之为纲目也。山阳济阴。同于被篡。然三国并立。而汉统犹在。则黜黄初而书章武。以正天下之大法。诸藩交争。而唐祀遂泯。则虽以晋岐之袭用天祜。而夷于逆梁。不在大书之例。此其设义究竟之同于陶也。不已明乎。今之欲自为者。苟可以如渊明。则斯已矣。欲立法者。苟可以如朱子。则斯已矣。今乃薄晦庵,渊明之义。遽欲掩而过之。多见其惑也。夫只书甲子或纪 本朝年月者。乃出于不用康熙之意。则取法乎渊明,晦庵。其例章章。又何云有所贬而弁髦先代之义也。设如是也。渊明未免为贬其累世臣事之晋。而朱子未免为弁髦君臣之义也。吾之所同者。同于渊明朱子。今虽得罪于薄渊明朱子而不为者。亦何恨乎。且以先代之义为言。何其脱口轻肆而曾前后之不顾也。吾潘南先生。遭世不幸。当冠屦倒置之辰。宋既亡而元入中国。正犹今日之事。不知先生于明未兴元未遁之前。尚遵用宋氏之年号欤。抑犹未欤。若其未也。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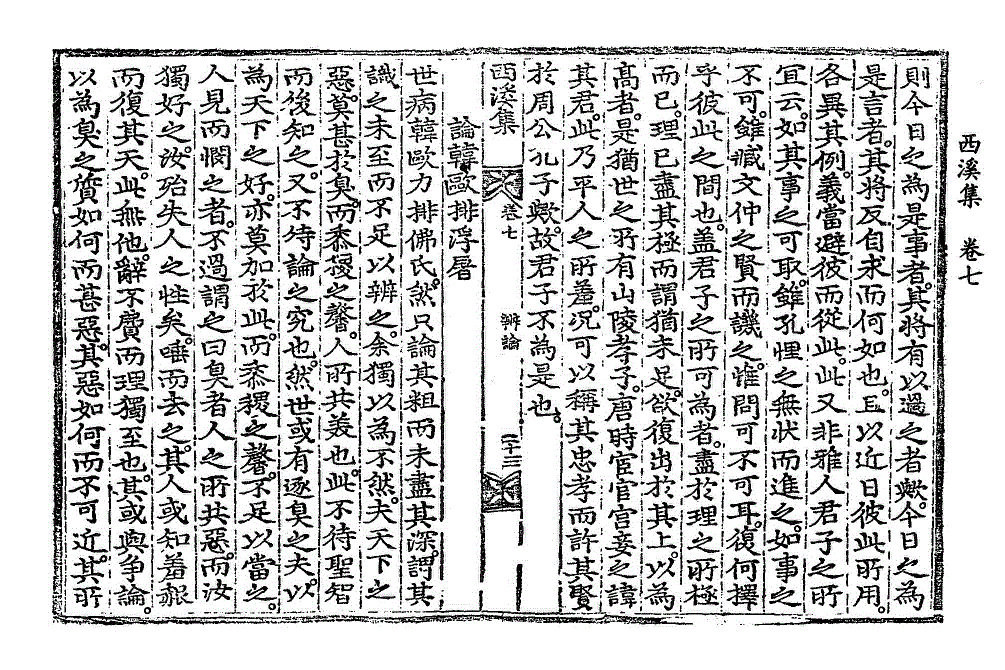 则今日之为是事者。其将有以过之者欤。今日之为是言者。其将反自求而何如也。且以近日彼此所用。各异其例。义当避彼而从此。此又非雅人君子之所宜云。如其事之可取。虽孔悝之无状而进之。如事之不可。虽臧文仲之贤而讥之。惟问可不可耳。复何择乎彼此之间也。盖君子之所可为者。尽于理之所极而已。理已尽其极而谓犹未足。欲复出于其上。以为高者。是犹世之所有山陵孝子。唐时宦官宫妾之讳其君。此乃平人之所羞。况可以称其忠孝而许其贤于周公孔子欤。故君子不为是也。
则今日之为是事者。其将有以过之者欤。今日之为是言者。其将反自求而何如也。且以近日彼此所用。各异其例。义当避彼而从此。此又非雅人君子之所宜云。如其事之可取。虽孔悝之无状而进之。如事之不可。虽臧文仲之贤而讥之。惟问可不可耳。复何择乎彼此之间也。盖君子之所可为者。尽于理之所极而已。理已尽其极而谓犹未足。欲复出于其上。以为高者。是犹世之所有山陵孝子。唐时宦官宫妾之讳其君。此乃平人之所羞。况可以称其忠孝而许其贤于周公孔子欤。故君子不为是也。论韩,欧排浮屠
世病韩欧力排佛氏。然只论其粗而未尽其深。谓其识之未至而不足以辨之。余独以为不然。夫天下之恶。莫甚于臭。而黍稷之馨。人所共美也。此不待圣智而后知之。又不待论之究也。然世或有逐臭之夫。以为天下之好。亦莫加于此。而黍稷之馨。不足以当之。人见而悯之者。不过谓之曰臭者人之所共恶。而汝独好之。汝殆失人之性矣。唾而去之。其人或知羞赧而复其天。此无他。辞不费而理独至也。其或与争论。以为臭之质如何而甚恶。其恶如何而不可近。其所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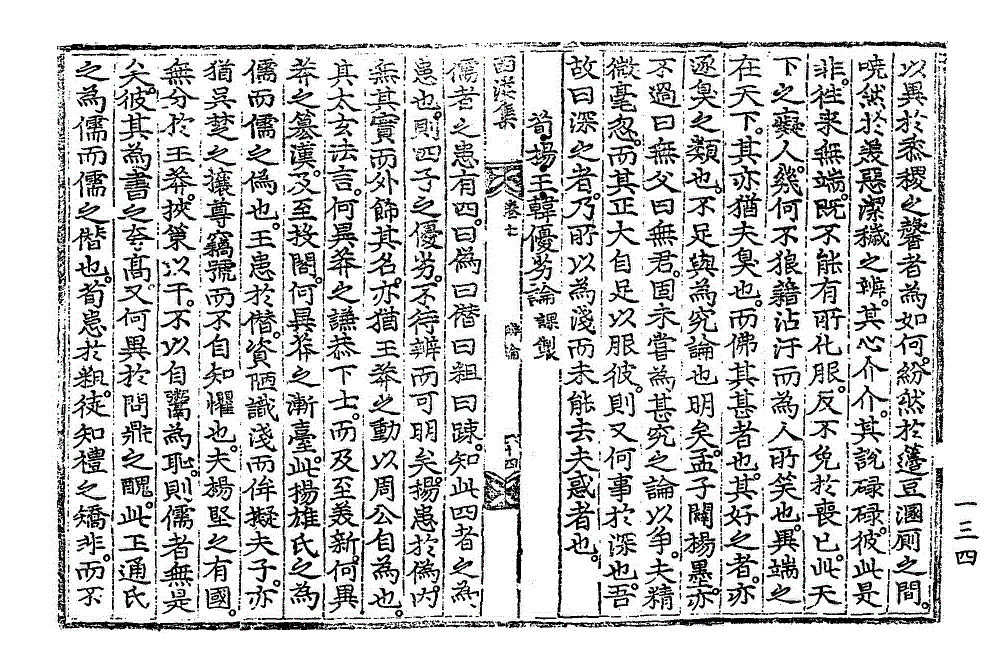 以异于黍稷之馨者为如何。纷然于笾豆溷厕之间。哓然于美恶洁秽之辨。其心介介。其说碌碌。彼此是非。往来无端。既不能有所化服。反不免于丧已。此天下之痴人。几何不狼藉沾污而为人所笑也。异端之在天下。其亦犹夫臭也。而佛其甚者也。其好之者。亦逐臭之类也。不足与为究论也明矣。孟子辟杨墨。亦不过曰无父曰无君。固未尝为甚究之论。以争夫精微毫忽。而其正大自足以服彼。则又何事于深也。吾故曰深之者。乃所以为浅而未能去夫惑者也。
以异于黍稷之馨者为如何。纷然于笾豆溷厕之间。哓然于美恶洁秽之辨。其心介介。其说碌碌。彼此是非。往来无端。既不能有所化服。反不免于丧已。此天下之痴人。几何不狼藉沾污而为人所笑也。异端之在天下。其亦犹夫臭也。而佛其甚者也。其好之者。亦逐臭之类也。不足与为究论也明矣。孟子辟杨墨。亦不过曰无父曰无君。固未尝为甚究之论。以争夫精微毫忽。而其正大自足以服彼。则又何事于深也。吾故曰深之者。乃所以为浅而未能去夫惑者也。荀,扬,王,韩优劣论(课制)
儒者之患有四。曰伪曰僭曰粗曰疏。知此四者之为患也。则四子之优劣。不待辨而可明矣。扬患于伪。内无其实而外饰其名。亦犹王莽之动以周公自为也。其太玄法言。何异莽之谦恭下士。而及至美新。何异莽之篡汉。及至投阁。何异莽之渐台。此扬雄氏之为儒而儒之伪也。王患于僭。资陋识浅而侔拟夫子。亦犹吴楚之攘尊窃号而不自知惧也。夫杨坚之有国。无分于王莽。挟策以干。不以自鬻为耻。则儒者无是矣。彼其为书之夸高。又何异于问鼎之丑。此王通氏之为儒而儒之僭也。荀患于粗。徒知礼之矫非。而不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5H 页
 识性之本善。徒识子弓之可师。而不知思孟之当尊。岂非所谓择焉而不精者耶。此荀卿氏之为儒而其粗者也。韩患于疏。徒见爱物之为仁。而不睹成己之是实。徒睹诚正之为学。而不见格致之为本。岂非所谓语焉而不详者耶。此韩愈氏之为儒而其疏者也。呜呼。伪与僭。班矣。而僭之罪。间于伪。疏与粗。等矣。而粗之失。大于疏。执是而观之。四子之优劣。其果有难辨者乎。
识性之本善。徒识子弓之可师。而不知思孟之当尊。岂非所谓择焉而不精者耶。此荀卿氏之为儒而其粗者也。韩患于疏。徒见爱物之为仁。而不睹成己之是实。徒睹诚正之为学。而不见格致之为本。岂非所谓语焉而不详者耶。此韩愈氏之为儒而其疏者也。呜呼。伪与僭。班矣。而僭之罪。间于伪。疏与粗。等矣。而粗之失。大于疏。执是而观之。四子之优劣。其果有难辨者乎。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序 十(一作九)首
穑经序
昔樊迟学稼圃于孔子。孔子辞以不如老农老圃。及其退而又责之以小人。使闻而知所愧。夫稼与圃。岂道之所不该。君子之所深绝而不为者乎。史言弃喜种树事。尧为后稷。孟子亦云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然则稼穑。固民生之本而天下之要道。圣人未尝废其术。至身亲修之以教人者。夫子何遽绝之哉。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处贱而为鄙事。事虽有鄙于稼圃者。亦夫子之所不免为之。况稼与圃也。固贱者之恒业而勉焉以孜孜者耶。圣人于事苟为之。必尽其方。事之鄙于稼圃者。且犹能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5L 页
 之。独不能于稼圃乎哉。稼圃者。固民之所重。圣人不应为之而怠其事荒其业也。樊迟盖亦知圣人之知之。故欲学之也。客或曰。夫子不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今拒迟若此者。其意安在。稼圃之与博奕。亦相去远矣。异哉。夫子之进博奕而退稼圃也。曰。非也。此夫子有为而谓之。非顾以博奕胜于稼圃也。今有行束脩挟书而请益者。夫子进而教之矣。如有操博奕而请益者。固不教之耳。非惟夫子之所不教。虽博奕者。亦不敢以至于夫子之门。如此者何。知不可故也。今迟学于圣人而请学稼圃。其意盖不以为不可。此其所以异也。夫子特以君子学道。务学其大。农圃小道。达之亦可。不达亦可。非君子之所务学。彼须也舍为其大而求其小。殆乎不可以进于道矣。故辞以责之如是也。然则稼圃。将不可学欤。曰。何为乎不可。为君子。学为君子。为野人。学为野人。素位而行。各务其业者也。学此其惟野人乎。然则于谁学而可也。曰。欲射者。必学于羿,逄蒙。欲御者。必学于造父,王良。如有欲弈者。则亦必之弈秋之门而学焉。今学为野人。而不求野人之能为吾师者而学之。可乎。夫子固告之矣。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孰为稼圃。孰求
之。独不能于稼圃乎哉。稼圃者。固民之所重。圣人不应为之而怠其事荒其业也。樊迟盖亦知圣人之知之。故欲学之也。客或曰。夫子不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今拒迟若此者。其意安在。稼圃之与博奕。亦相去远矣。异哉。夫子之进博奕而退稼圃也。曰。非也。此夫子有为而谓之。非顾以博奕胜于稼圃也。今有行束脩挟书而请益者。夫子进而教之矣。如有操博奕而请益者。固不教之耳。非惟夫子之所不教。虽博奕者。亦不敢以至于夫子之门。如此者何。知不可故也。今迟学于圣人而请学稼圃。其意盖不以为不可。此其所以异也。夫子特以君子学道。务学其大。农圃小道。达之亦可。不达亦可。非君子之所务学。彼须也舍为其大而求其小。殆乎不可以进于道矣。故辞以责之如是也。然则稼圃。将不可学欤。曰。何为乎不可。为君子。学为君子。为野人。学为野人。素位而行。各务其业者也。学此其惟野人乎。然则于谁学而可也。曰。欲射者。必学于羿,逄蒙。欲御者。必学于造父,王良。如有欲弈者。则亦必之弈秋之门而学焉。今学为野人。而不求野人之能为吾师者而学之。可乎。夫子固告之矣。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孰为稼圃。孰求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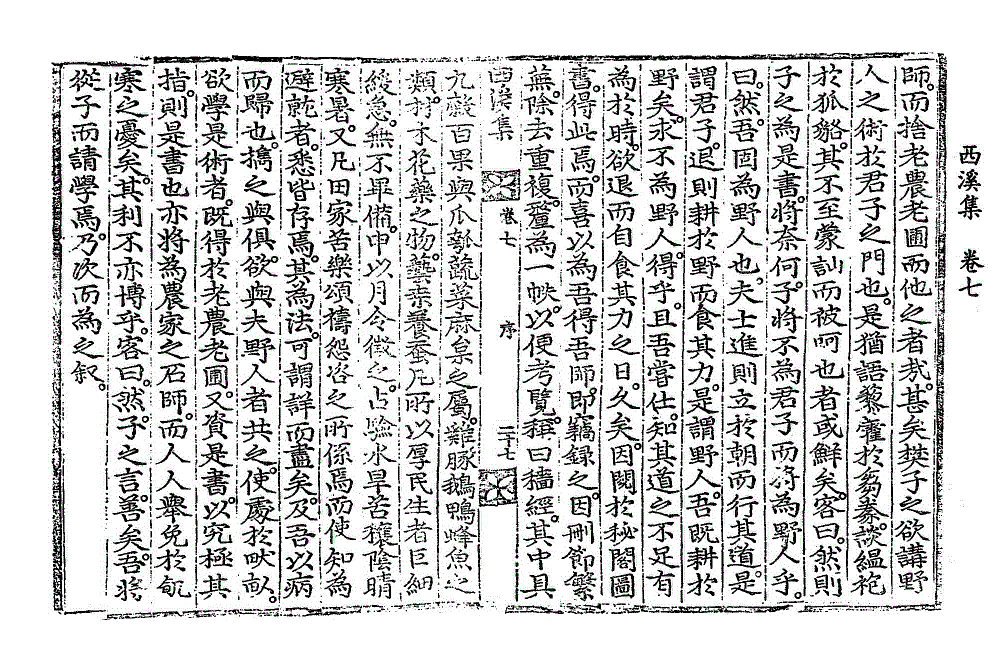 师。而舍老农老圃而他之者哉。甚矣樊子之欲讲野人之术于君子之门也。是犹语藜藿于刍豢。谈缊袍于狐貉。其不至蒙讪而被呵也者或鲜矣。客曰。然则子之为是书。将奈何。子将不为君子而将为野人乎。曰。然。吾固为野人也。夫士进则立于朝而行其道。是谓君子。退则耕于野而食其力。是谓野人。吾既耕于野矣。求不为野人。得乎。且吾尝仕。知其道之不足有为于时。欲退而自食其力之日。久矣。因阅于秘阁图书。得此焉。而喜以为吾得吾师。即窃录之。因删节繁芜。除去重复。釐为一帙。以便考览。称曰穑经。其中具九谷百果与瓜瓠蔬菜麻枲之属。鸡豚鹅鸭蜂鱼之类。材木花药之物。艺桑养蚕凡所以厚民生者巨细缓急。无不毕备。申以月令徵之。占验水早苦穰阴晴寒暑。又凡田家苦乐颂祷怨咨之所系焉而使知为避就者。悉皆存焉。其为法。可谓详而尽矣。及吾以病而归也。携之与俱。欲与夫野人者共之。使处于畎亩。欲学是术者。既得于老农老圃。又资是书。以究极其指。则是书也亦将为农家之石师。而人人举免于饥寒之忧矣。其利不亦博乎。客曰。然。子之言。善矣。吾将从子而请学焉。乃次而为之叙。
师。而舍老农老圃而他之者哉。甚矣樊子之欲讲野人之术于君子之门也。是犹语藜藿于刍豢。谈缊袍于狐貉。其不至蒙讪而被呵也者或鲜矣。客曰。然则子之为是书。将奈何。子将不为君子而将为野人乎。曰。然。吾固为野人也。夫士进则立于朝而行其道。是谓君子。退则耕于野而食其力。是谓野人。吾既耕于野矣。求不为野人。得乎。且吾尝仕。知其道之不足有为于时。欲退而自食其力之日。久矣。因阅于秘阁图书。得此焉。而喜以为吾得吾师。即窃录之。因删节繁芜。除去重复。釐为一帙。以便考览。称曰穑经。其中具九谷百果与瓜瓠蔬菜麻枲之属。鸡豚鹅鸭蜂鱼之类。材木花药之物。艺桑养蚕凡所以厚民生者巨细缓急。无不毕备。申以月令徵之。占验水早苦穰阴晴寒暑。又凡田家苦乐颂祷怨咨之所系焉而使知为避就者。悉皆存焉。其为法。可谓详而尽矣。及吾以病而归也。携之与俱。欲与夫野人者共之。使处于畎亩。欲学是术者。既得于老农老圃。又资是书。以究极其指。则是书也亦将为农家之石师。而人人举免于饥寒之忧矣。其利不亦博乎。客曰。然。子之言。善矣。吾将从子而请学焉。乃次而为之叙。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6L 页
 送金象卿之岭东诗序
送金象卿之岭东诗序金君梦臣象卿。其先子吾友也。其伯父吾以兄事之。象卿又与吾之子友。其女弟又嫁吾子为妇。象卿先子。与吾生年差一岁。而吾子之与象卿。又如吾之与其先子焉。象卿伯父与先子。既下世。惟象卿与吾往还。两世之交。重婚媾焉。象卿于吾。亲且密可知也。生见时事之多虞。约与其内外群从。挈家踰岭东。之海上。隐处焉。吾以一二年间外忧之必至。尚未可料。又惜其远去而失所亲也。劝止之。谓众乡姑徐以观。象卿不从。既且往矣。来告余于别。吾虽不能沮其行。又喜生之虑患。预执志决。能不挠于人。而动先于几。殆不可及也。若吾之盘桓却顾。智不出于朝夕者。大有愧乎。吾谓象卿子且先。吾从而后焉。异日东道。吾以子为主矣。为赋诗以送之。
徵士记中深寄意。隐居恨未远风尘。凭君遍访浮花水。穷峡宁无避役人。
举世同忧同不去。惟君轻举独超然。海山正有栖身地。应念风波坐漏船。
游水落山诗后序
三角,道峰。近都之雄。与夫水落鼎峙而尊。故能使四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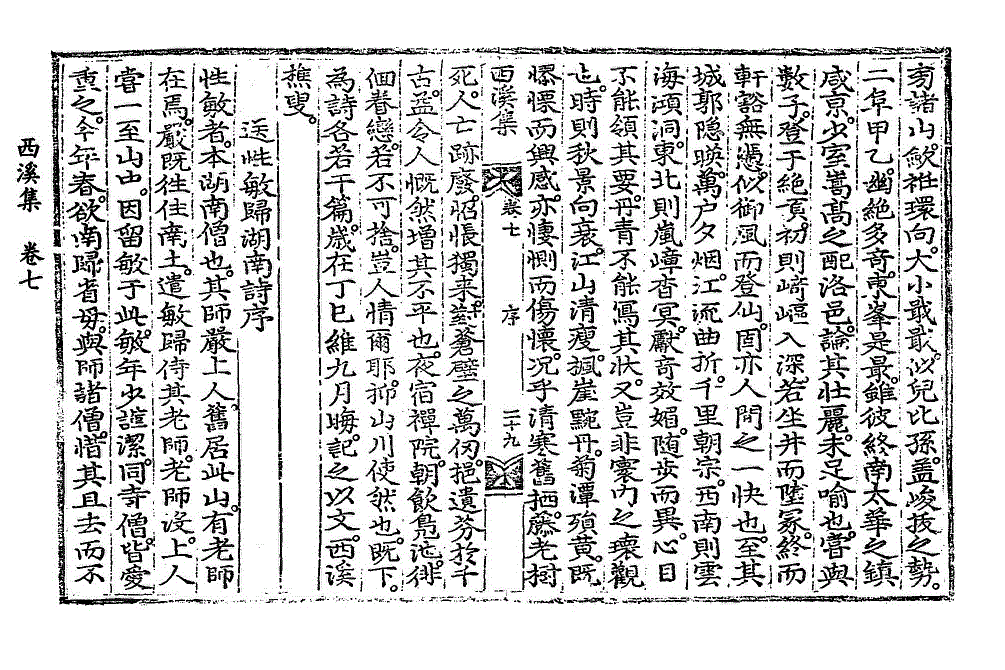 旁诸山。敛衽环向。大小戢戢。似儿比孙。盖峻拔之势。二阜甲乙。幽绝多奇。东峰是最。虽彼终南太华之镇咸京。少室嵩高之配洛邑。论其壮丽。未足喻也。尝与数子。登于绝顶。初则崎岖入深。若坐井而堕冢。终而轩豁无凭。似御风而登仙。固亦人间之一快也。至其城郭隐映。万户夕烟。江流曲折。千里朝宗。西南则云海澒洞。东北则岚嶂杳冥。献奇效媚。随步而异。心目不能领其要。丹青不能写其状。又岂非寰内之瑰观也。时则秋景向衰。江山清瘦。枫崖黦丹。菊潭殒黄。既憀慄而兴感。亦悽恻而伤怀。况乎清寒旧迁。藤老树死。人亡迹废。怊怅独来。对苍壁之万仞。挹遗芬于千古。益令人慨然增其不平也。夜宿禅院。朝饮凫池。徘佪眷恋。若不可舍。岂人情尔耶。抑山川使然也。既下。为诗各若干篇。岁在丁巳维九月晦。记之以文。西溪樵叟。
旁诸山。敛衽环向。大小戢戢。似儿比孙。盖峻拔之势。二阜甲乙。幽绝多奇。东峰是最。虽彼终南太华之镇咸京。少室嵩高之配洛邑。论其壮丽。未足喻也。尝与数子。登于绝顶。初则崎岖入深。若坐井而堕冢。终而轩豁无凭。似御风而登仙。固亦人间之一快也。至其城郭隐映。万户夕烟。江流曲折。千里朝宗。西南则云海澒洞。东北则岚嶂杳冥。献奇效媚。随步而异。心目不能领其要。丹青不能写其状。又岂非寰内之瑰观也。时则秋景向衰。江山清瘦。枫崖黦丹。菊潭殒黄。既憀慄而兴感。亦悽恻而伤怀。况乎清寒旧迁。藤老树死。人亡迹废。怊怅独来。对苍壁之万仞。挹遗芬于千古。益令人慨然增其不平也。夜宿禅院。朝饮凫池。徘佪眷恋。若不可舍。岂人情尔耶。抑山川使然也。既下。为诗各若干篇。岁在丁巳维九月晦。记之以文。西溪樵叟。送性敏归湖南诗序
性敏者。本湖南僧也。其师严上人。旧居此山。有老师在焉。严既往住南土。遣敏归侍其老师。老师没。上人尝一至山中。因留敏于此。敏年少谨洁。同寺僧。皆爱重之。今年春。欲南归省母与。师诸僧惜其且去而不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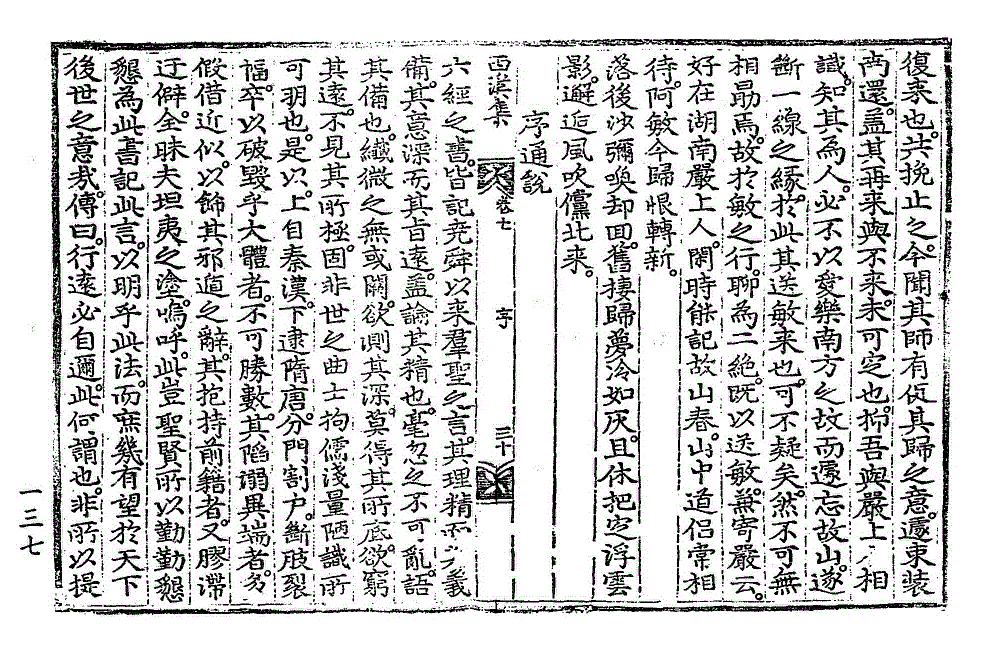 复来也。共挽止之。今闻其师有促其归之意。遽束装南还。盖其再来与不来。未可定也。抑吾与严上人相识。知其为人。必不以爱乐南方之故而遽忘故山。遂断一线之缘。于此其送敏。来也可不疑矣。然不可无相勖焉。故于敏之行。聊为二绝。既以送敏。兼寄严云。好在湖南严上人。闲时能记故山春。山中道侣常相待。阿敏今归恨转新。
复来也。共挽止之。今闻其师有促其归之意。遽束装南还。盖其再来与不来。未可定也。抑吾与严上人相识。知其为人。必不以爱乐南方之故而遽忘故山。遂断一线之缘。于此其送敏。来也可不疑矣。然不可无相勖焉。故于敏之行。聊为二绝。既以送敏。兼寄严云。好在湖南严上人。闲时能记故山春。山中道侣常相待。阿敏今归恨转新。落后沙弥唤却回。旧栖归梦冷如灰。且休把定浮云影。邂逅风吹傥北来。
序通说
六经之书。皆记尧舜以来群圣之言。其理精而其义备。其意深而其旨远。盖论其精也。毫忽之不可乱。语其备也。纤微之无或阙。欲测其深。莫得其所底。欲穷其远。不见其所极。固非世之曲士拘儒浅量陋识所可明也。是以。上自秦汉。下逮隋唐。分门割户。断肢裂幅。卒以破毁乎大体者。不可胜数。其陷溺异端者。多假借近似。以饰其邪遁之辞。其抱持前籍者。又胶滞迂僻。全昧夫坦夷之涂。呜呼。此岂圣贤所以勤勤恳恳为此书记此言。以明乎此法。而庶几有望于天下后世之意哉。传曰。行远必自迩。此何谓也。非所以提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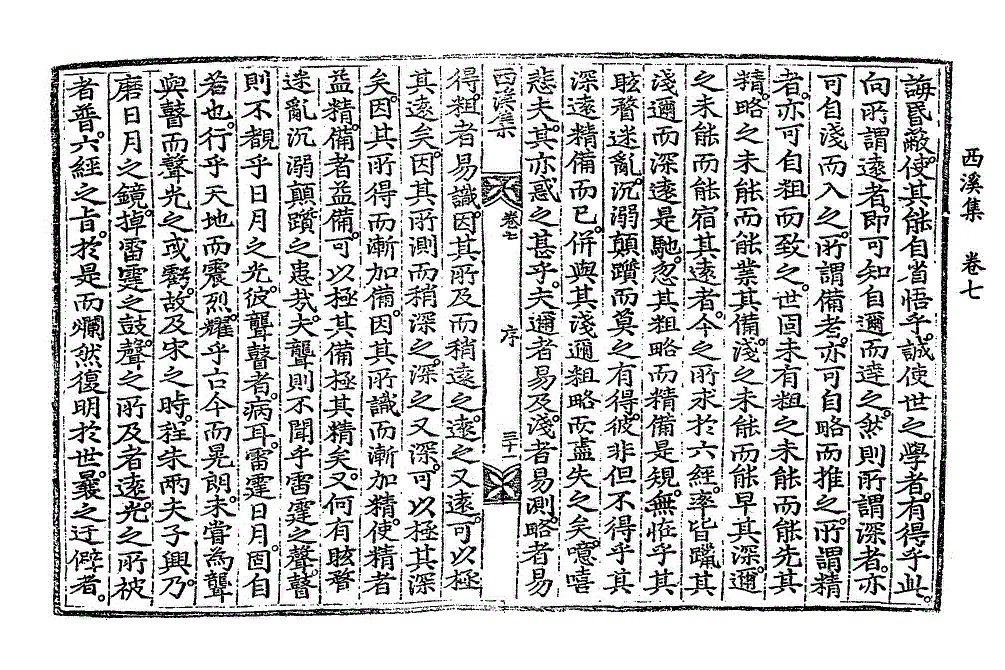 诲昏蔽。使其能自省悟乎。诚使世之学者。有得乎此。向所谓远者。即可知自迩而达之。然则所谓深者。亦可自浅而入之。所谓备者。亦可自略而推之。所谓精者。亦可自粗而致之。世固未有粗之未能而能先其精。略之未能而能业其备。浅之未能而能早其深。迩之未能而能宿其远者。今之所求于六经。率皆躐其浅迩而深远是驰。忽其粗略而精备是规。无怪乎其眩瞀迷乱。沈溺颠踬而莫之有得。彼非但不得乎其深远精备而已。并与其浅迩粗略而尽失之矣。噫嘻悲夫。其亦惑之甚乎。夫迩者易及。浅者易测。略者易得。粗者易识。因其所及而稍远之。远之又远。可以极其远矣。因其所测而稍深之。深之又深。可以极其深矣。因其所得而渐加备。因其所识而渐加精。使精者益精。备者益备。可以极其备极其精矣。又何有眩瞀迷乱沈溺颠踬之患哉。夫聋则不闻乎雷霆之声。瞽则不睹乎日月之光。彼聋瞽者。病耳。雷霆日月。固自若也。行乎天地而震烈。耀乎古今而晃朗。未尝为聋与瞽而声光之或亏。故及宋之时。程朱两夫子兴。乃磨日月之镜。掉雷霆之鼓。声之所及者远。光之所被者普。六经之旨。于是而烂然复明于世。曩之迂僻者。
诲昏蔽。使其能自省悟乎。诚使世之学者。有得乎此。向所谓远者。即可知自迩而达之。然则所谓深者。亦可自浅而入之。所谓备者。亦可自略而推之。所谓精者。亦可自粗而致之。世固未有粗之未能而能先其精。略之未能而能业其备。浅之未能而能早其深。迩之未能而能宿其远者。今之所求于六经。率皆躐其浅迩而深远是驰。忽其粗略而精备是规。无怪乎其眩瞀迷乱。沈溺颠踬而莫之有得。彼非但不得乎其深远精备而已。并与其浅迩粗略而尽失之矣。噫嘻悲夫。其亦惑之甚乎。夫迩者易及。浅者易测。略者易得。粗者易识。因其所及而稍远之。远之又远。可以极其远矣。因其所测而稍深之。深之又深。可以极其深矣。因其所得而渐加备。因其所识而渐加精。使精者益精。备者益备。可以极其备极其精矣。又何有眩瞀迷乱沈溺颠踬之患哉。夫聋则不闻乎雷霆之声。瞽则不睹乎日月之光。彼聋瞽者。病耳。雷霆日月。固自若也。行乎天地而震烈。耀乎古今而晃朗。未尝为聋与瞽而声光之或亏。故及宋之时。程朱两夫子兴。乃磨日月之镜。掉雷霆之鼓。声之所及者远。光之所被者普。六经之旨。于是而烂然复明于世。曩之迂僻者。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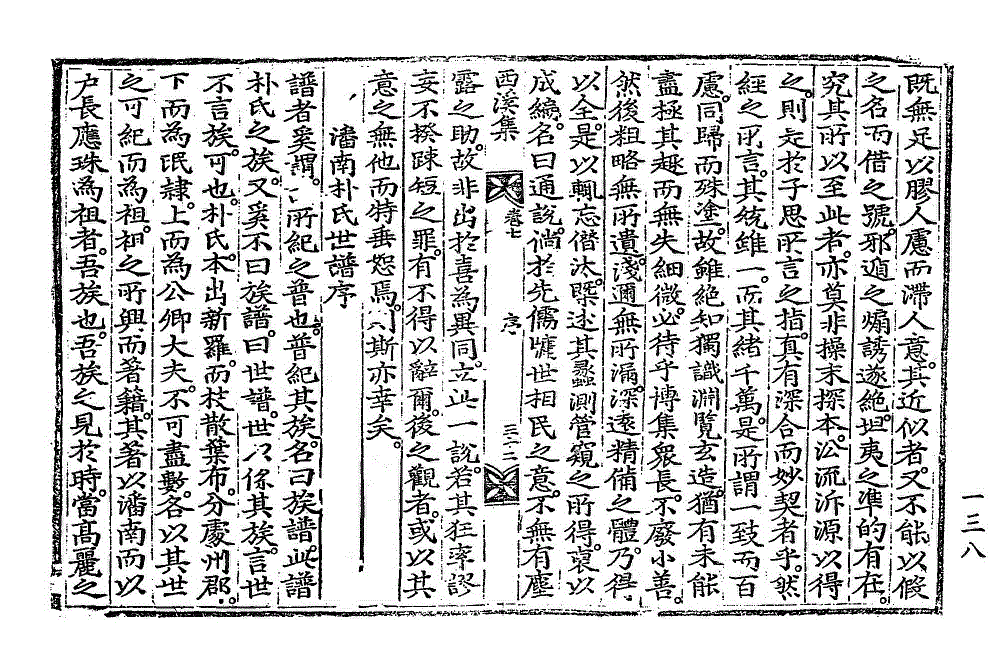 既无足以胶人虑而滞人意。其近似者。又不能以假之名而借之号。邪遁之煽诱遂绝。坦夷之准的有在。究其所以至此者。亦莫非操末探本。沿流溯源以得之。则是于子思所言之指。真有深合而妙契者乎。然经之所言。其统虽一。而其绪千万。是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故虽绝知独识渊览玄造。犹有未能尽极其趣而无失细微。必待乎博集众长。不废小善。然后粗略无所遗。浅迩无所漏。深远精备之体。乃得以全。是以辄忘僭汰。槩述其蠡测管窥之所得。裒以成编。名曰通说。倘于先儒牖世相民之意。不无有尘露之助。故非出于喜为异同。立此一说。若其狂率谬妄不揆疏短之罪。有不得以辞尔。后之观者。或以其意之无他而特垂恕焉。则斯亦幸矣。
既无足以胶人虑而滞人意。其近似者。又不能以假之名而借之号。邪遁之煽诱遂绝。坦夷之准的有在。究其所以至此者。亦莫非操末探本。沿流溯源以得之。则是于子思所言之指。真有深合而妙契者乎。然经之所言。其统虽一。而其绪千万。是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故虽绝知独识渊览玄造。犹有未能尽极其趣而无失细微。必待乎博集众长。不废小善。然后粗略无所遗。浅迩无所漏。深远精备之体。乃得以全。是以辄忘僭汰。槩述其蠡测管窥之所得。裒以成编。名曰通说。倘于先儒牖世相民之意。不无有尘露之助。故非出于喜为异同。立此一说。若其狂率谬妄不揆疏短之罪。有不得以辞尔。后之观者。或以其意之无他而特垂恕焉。则斯亦幸矣。潘南朴氏世谱序
谱者奚谓。谓所纪之普也。普纪其族。名曰族谱。此谱朴氏之族。又奚不曰族谱。曰世谱。世以系其族。言世不言族。可也。朴氏。本出新罗。而枝散叶布。分处州郡。下而为氓隶。上而为公卿大夫。不可尽数。各以其世之可纪而为祖。相之所兴而著籍。其著以潘南而以户长应珠为祖者。吾族也。吾族之见于时。当高丽之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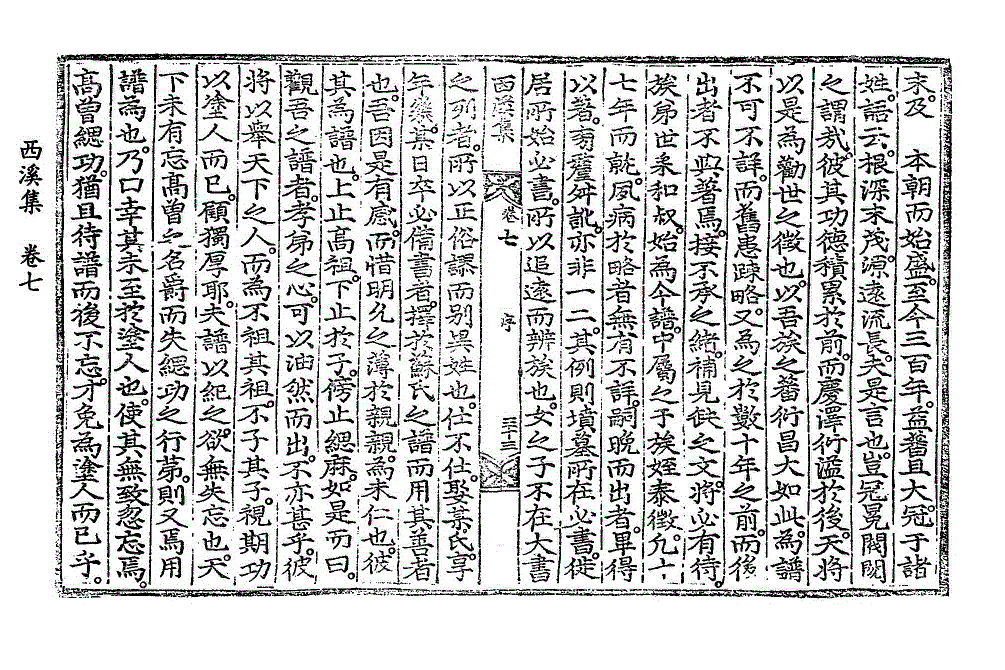 末。及 本朝而始盛。至今三百年。益蕃且大。冠于诸姓。语云。根深末茂。源远流长。夫是言也。岂冠冕阀阅之谓哉。彼其功德积累于前。而庆泽衍溢于后。天将以是为劝世之徵也。以吾族之蕃衍昌大如此。为谱不可不详。而旧患疏略。又为之于数十年之前。而后出者不与著焉。接不承之绪。补见缺之文。将必有待。族弟世采和叔。始为今谱。中属之于族侄泰徵。凡十七年而就。夙病于略者无有不详。嗣晚而出者。毕得以著。旁釐舛讹。亦非一二。其例则坟墓所在必书。徙居所始必书。所以追远而辨族也。女之子不在大书之列者。所以正俗谬而别异姓也。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必备书者。择于苏氏之谱而用其善者也。吾因是有感。而惜明允之薄于亲亲。为未仁也。彼其为谱也。上止高祖。下止于子。傍止缌麻。如是而曰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出。不亦甚乎。彼将以举天下之人。而为不祖其祖。不子其子。视期功以涂人而已。顾独厚耶。夫谱以纪之。欲无失忘也。天下未有忘高曾之名爵而失缌功之行第。则又焉用谱为也。乃曰幸其未至于涂人也。使其无致忽忘焉。高曾缌功。犹且待谱而后不忘。才免为涂人而已乎。
末。及 本朝而始盛。至今三百年。益蕃且大。冠于诸姓。语云。根深末茂。源远流长。夫是言也。岂冠冕阀阅之谓哉。彼其功德积累于前。而庆泽衍溢于后。天将以是为劝世之徵也。以吾族之蕃衍昌大如此。为谱不可不详。而旧患疏略。又为之于数十年之前。而后出者不与著焉。接不承之绪。补见缺之文。将必有待。族弟世采和叔。始为今谱。中属之于族侄泰徵。凡十七年而就。夙病于略者无有不详。嗣晚而出者。毕得以著。旁釐舛讹。亦非一二。其例则坟墓所在必书。徙居所始必书。所以追远而辨族也。女之子不在大书之列者。所以正俗谬而别异姓也。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必备书者。择于苏氏之谱而用其善者也。吾因是有感。而惜明允之薄于亲亲。为未仁也。彼其为谱也。上止高祖。下止于子。傍止缌麻。如是而曰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出。不亦甚乎。彼将以举天下之人。而为不祖其祖。不子其子。视期功以涂人而已。顾独厚耶。夫谱以纪之。欲无失忘也。天下未有忘高曾之名爵而失缌功之行第。则又焉用谱为也。乃曰幸其未至于涂人也。使其无致忽忘焉。高曾缌功。犹且待谱而后不忘。才免为涂人而已乎。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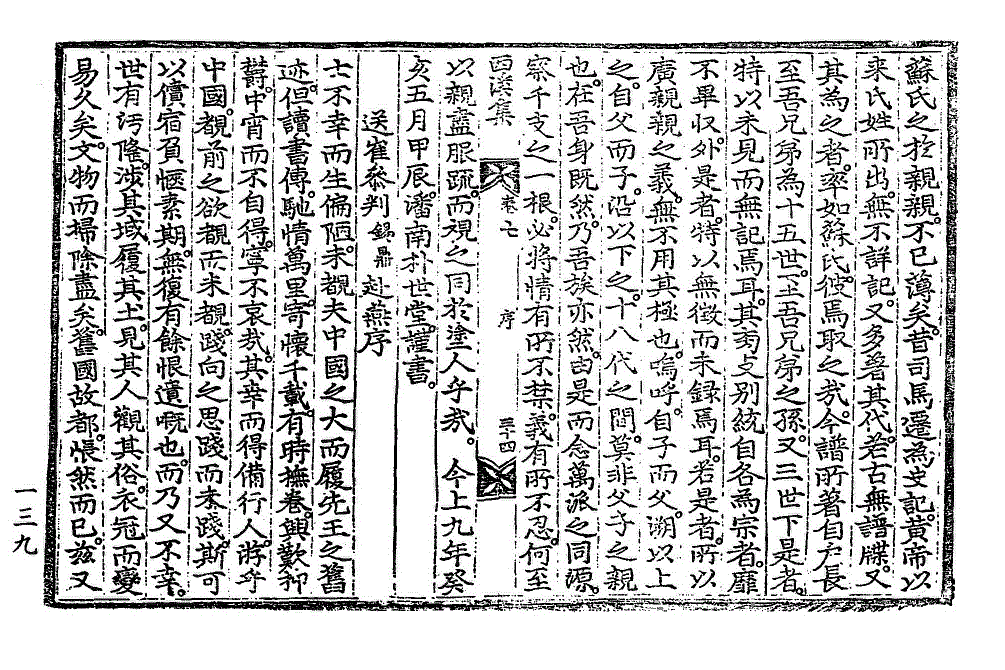 苏氏之于亲亲。不已薄矣。昔司马迁为史记。黄帝以来氏姓所出。无不详记。又多著其代。若古无谱牒。又其为之者。率如苏氏。彼焉取之哉。今谱所著自户长至吾兄弟为十五世。至吾兄弟之孙。又三世。下是者。特以未见而无记焉耳。其旁支别统自各为宗者。靡不毕收。外是者。特以无徵而未录焉耳。若是者。所以广亲亲之义。无不用其极也。呜呼。自子而父。溯以上之。自父而子。沿以下之。十八代之间。莫非父子之亲也。在吾身既然。乃吾族亦然。由是而念万派之同源。察千支之一根。必将情有所不禁。义有所不忍。何至以亲尽服疏。而视之同于涂人乎哉。 今上九年癸亥五月甲辰。潘南朴世堂。谨书。
苏氏之于亲亲。不已薄矣。昔司马迁为史记。黄帝以来氏姓所出。无不详记。又多著其代。若古无谱牒。又其为之者。率如苏氏。彼焉取之哉。今谱所著自户长至吾兄弟为十五世。至吾兄弟之孙。又三世。下是者。特以未见而无记焉耳。其旁支别统自各为宗者。靡不毕收。外是者。特以无徵而未录焉耳。若是者。所以广亲亲之义。无不用其极也。呜呼。自子而父。溯以上之。自父而子。沿以下之。十八代之间。莫非父子之亲也。在吾身既然。乃吾族亦然。由是而念万派之同源。察千支之一根。必将情有所不禁。义有所不忍。何至以亲尽服疏。而视之同于涂人乎哉。 今上九年癸亥五月甲辰。潘南朴世堂。谨书。送崔参判(锡鼎)赴燕序
士不幸而生偏陋。未睹夫中国之大而履先王之旧迹。但读书传。驰情万里。寄怀千载。有时抚卷。兴叹抑郁。中宵而不自得。宁不哀哉。其幸而得备行人。游乎中国。睹前之欲睹而未睹。践向之思践而未践。斯可以偿宿负惬素期。无复有馀恨遗嘅也。而乃又不幸。世有污隆。涉其域履其土。见其人观其俗。衣冠而变易久矣。文物而扫除尽矣。旧国故都。怅然而已。玆又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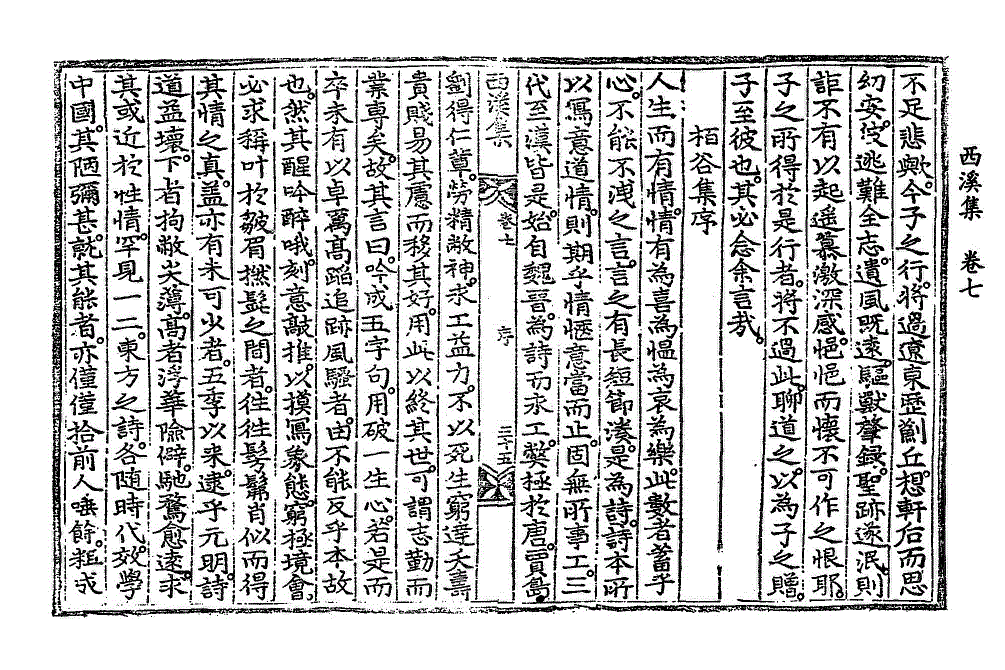 不足悲欤。今子之行。将过辽东历蓟丘。想轩后而思幼安。彼逃难全志。遗风既远。驱兽肇录。圣迹遂泯。则讵不有以起遥慕激深感。悒悒而怀不可作之恨耶。子之所得于是行者。将不过此。聊道之。以为子之赠。子至彼也。其必念余言哉。
不足悲欤。今子之行。将过辽东历蓟丘。想轩后而思幼安。彼逃难全志。遗风既远。驱兽肇录。圣迹遂泯。则讵不有以起遥慕激深感。悒悒而怀不可作之恨耶。子之所得于是行者。将不过此。聊道之。以为子之赠。子至彼也。其必念余言哉。柏谷集序
人生而有情。情有为喜为愠为哀为乐。此数者蓄乎心。不能不泄之言。言之有长短节凑。是为诗。诗本所以写意道情。则期乎情惬意当而止。固无所事工。三代至汉皆是。始自魏晋。为诗而求工。弊极于唐。贾岛,刘得仁辈。劳精敝神。求工益力。不以死生穷达夭寿贵贱易其虑而移其好。用此以终其世。可谓志勤而业专矣。故其言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若是而卒未有以卓厉高蹈追迹风骚者。由不能反乎本故也。然其醒吟醉哦。刻意敲推。以摸写象态。穷极境会必求称叶于皱眉撚髭之间者。往往髣髴肖似而得其情之真。盖亦有未可少者。五季以来。逮乎元明。诗道益坏。下者拘敝尖薄。高者浮华险僻。驰骛愈远。求其或近于性情。罕见一二。东方之诗。各随时代。效学中国。其陋弥甚。就其能者。亦仅仅拾前人唾馀。粗成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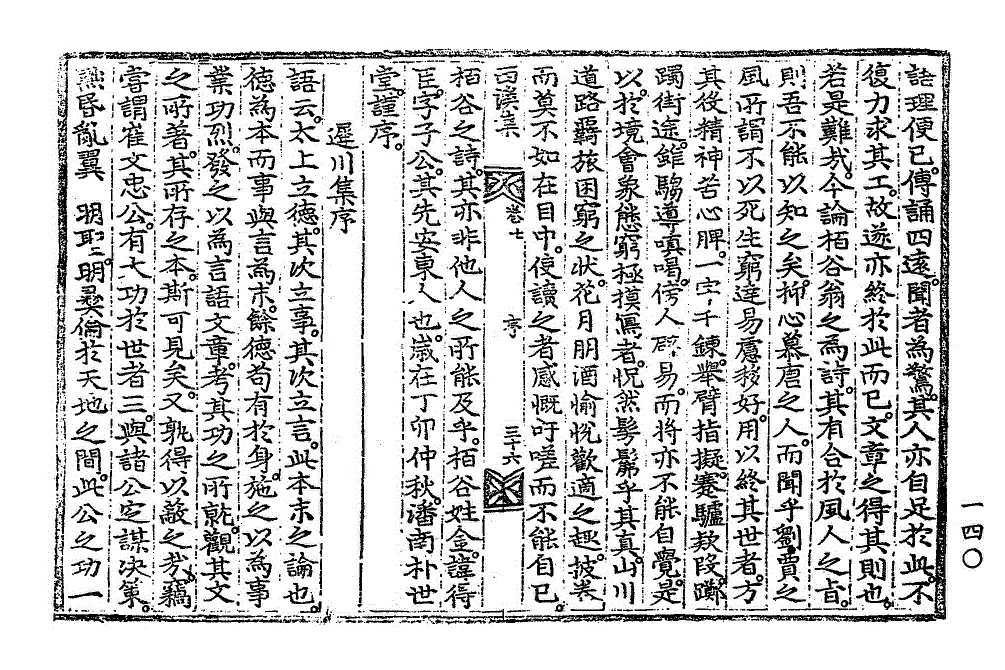 语理便已。传诵四远。闻者为惊。其人亦自足于此。不复力求其工。故遂亦终于此而巳。文章之得其则也若是难哉。今论柏谷翁之为诗。其有合于风人之旨。则吾不能以知之矣。抑心慕唐之人。而闻乎刘,贾之风所谓不以死生穷达易虑移好。用以终其世者。方其役精神苦心脾。一字千鍊。举臂指拟。蹇驴款段。踯躅街途。虽驺道嗔喝。傍人辟易。而将亦不能自觉。是以。于境会象态穷极摸写者。恍然髣髴乎其真。山川道路羁旅困穷之状。花月朋酒愉悦欢适之趣。披卷而莫不如在目中。使读之者感慨吁嗟而不能自已。柏谷之诗。其亦非他人之所能及乎。柏谷姓金。讳得臣。字子公。其先安东人也。岁在丁卯仲秋。潘南朴世堂。谨序。
语理便已。传诵四远。闻者为惊。其人亦自足于此。不复力求其工。故遂亦终于此而巳。文章之得其则也若是难哉。今论柏谷翁之为诗。其有合于风人之旨。则吾不能以知之矣。抑心慕唐之人。而闻乎刘,贾之风所谓不以死生穷达易虑移好。用以终其世者。方其役精神苦心脾。一字千鍊。举臂指拟。蹇驴款段。踯躅街途。虽驺道嗔喝。傍人辟易。而将亦不能自觉。是以。于境会象态穷极摸写者。恍然髣髴乎其真。山川道路羁旅困穷之状。花月朋酒愉悦欢适之趣。披卷而莫不如在目中。使读之者感慨吁嗟而不能自已。柏谷之诗。其亦非他人之所能及乎。柏谷姓金。讳得臣。字子公。其先安东人也。岁在丁卯仲秋。潘南朴世堂。谨序。迟川集序
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事。其次立言。此本末之论也。德为本而事与言为末。馀德苟有于身。施之以为事业功烈。发之以为言语文章。考其功之所就。观其文之所著。其所存之本。斯可见矣。又孰得以蔽之哉。窃尝谓崔文忠公。有大功于世者三。与诸公定谋决策。黜昏乱翼 明圣。明彝伦于天地之间。此公之功一
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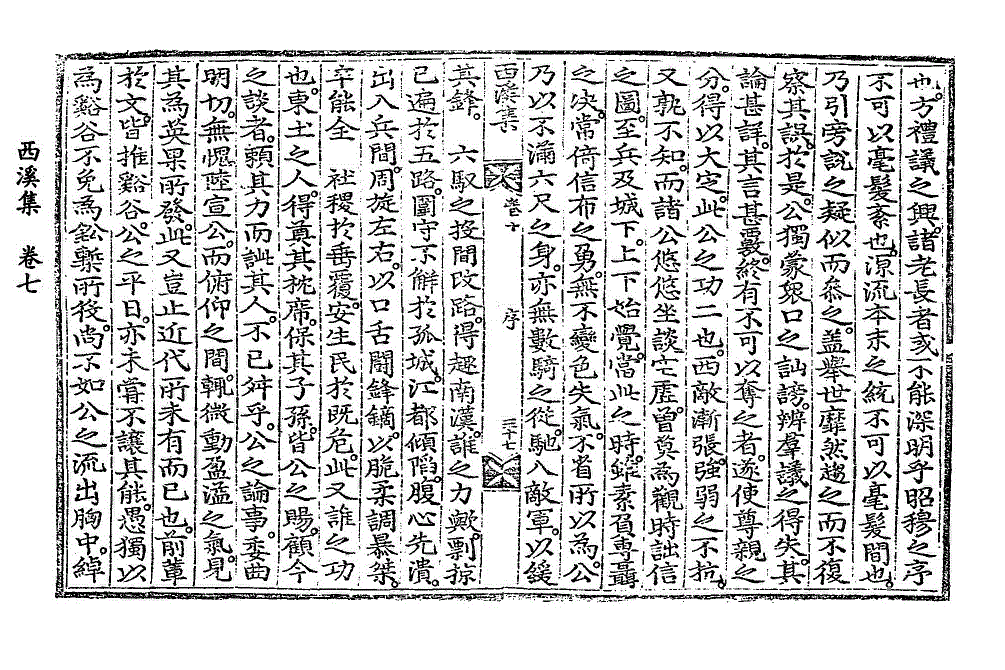 也。方礼议之兴。诸老长者或不能深明乎昭穆之序不可以毫发紊也。源流本末之统不可以毫发间也。乃引旁说之疑似而参之。盖举世靡然趋之而不复察其误。于是。公独蒙众口之讪谤。辨群议之得失。其论甚详。其言甚覈。终有不可以夺之者。遂使尊亲之分。得以大定。此公之功二也。西敌渐张。强弱之不抗。又孰不知。而诸公悠悠坐谈空虚。曾莫为观时诎信之图。至兵及城下。上下始觉。当此之时。虽素负专聂之决。当倚信布之勇。无不变色失气。不省所以为。公乃以不满六尺之身。亦无数骑之从。驰入敌军。以缓其锋。 六驭之投间改路。得趣南汉。谁之力欤。剽掠已遍于五路。围守不解于孤城。江都倾陷。腹心先溃。出入兵间。周旋左右。以口舌斗锋镝。以脆柔调暴桀。卒能全 社稷于垂覆。安生民于既危。此又谁之功也。东土之人。得奠其枕席。保其子孙。皆公之赐。顾今之谈者。赖其力而訾其人。不已舛乎。公之论事。委曲明切。无愧陆宣公。而俯仰之间。辄微动盈溢之气。见其为英果所发。此又岂止近代所未有而已也。前辈于文。皆推溪谷。公之平日。亦未尝不让其能。愚独以为溪谷不免为铅椠所役。尚不如公之流出胸中。绰
也。方礼议之兴。诸老长者或不能深明乎昭穆之序不可以毫发紊也。源流本末之统不可以毫发间也。乃引旁说之疑似而参之。盖举世靡然趋之而不复察其误。于是。公独蒙众口之讪谤。辨群议之得失。其论甚详。其言甚覈。终有不可以夺之者。遂使尊亲之分。得以大定。此公之功二也。西敌渐张。强弱之不抗。又孰不知。而诸公悠悠坐谈空虚。曾莫为观时诎信之图。至兵及城下。上下始觉。当此之时。虽素负专聂之决。当倚信布之勇。无不变色失气。不省所以为。公乃以不满六尺之身。亦无数骑之从。驰入敌军。以缓其锋。 六驭之投间改路。得趣南汉。谁之力欤。剽掠已遍于五路。围守不解于孤城。江都倾陷。腹心先溃。出入兵间。周旋左右。以口舌斗锋镝。以脆柔调暴桀。卒能全 社稷于垂覆。安生民于既危。此又谁之功也。东土之人。得奠其枕席。保其子孙。皆公之赐。顾今之谈者。赖其力而訾其人。不已舛乎。公之论事。委曲明切。无愧陆宣公。而俯仰之间。辄微动盈溢之气。见其为英果所发。此又岂止近代所未有而已也。前辈于文。皆推溪谷。公之平日。亦未尝不让其能。愚独以为溪谷不免为铅椠所役。尚不如公之流出胸中。绰西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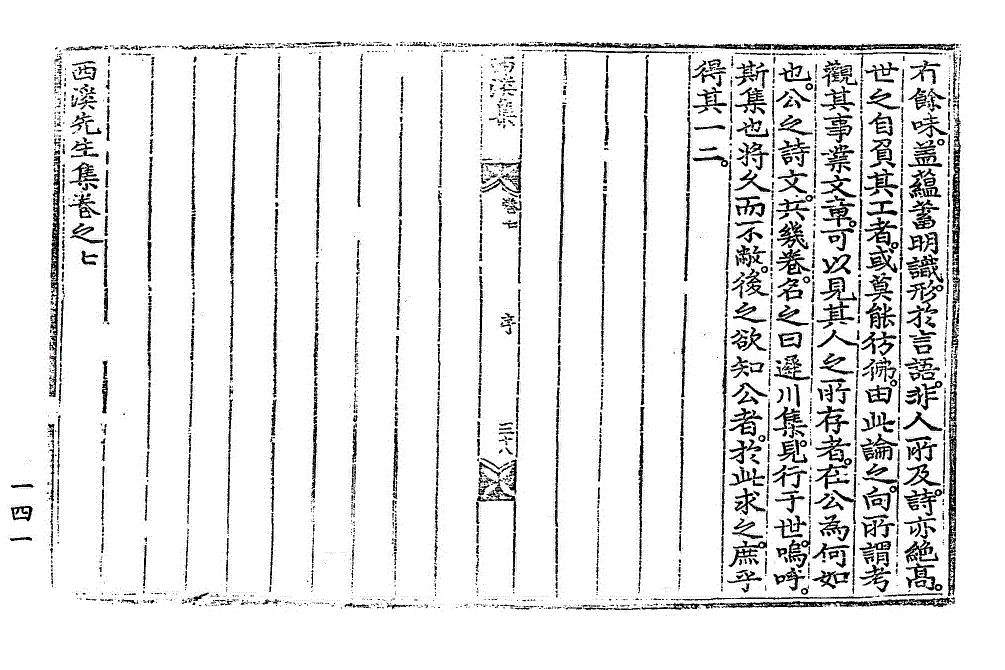 有馀味。盖蕴蓄明识。形于言语。非人所及。诗亦绝高。世之自负其工者。或莫能彷佛。由此论之。向所谓考观其事业文章。可以见其人之所存者。在公为何如也。公之诗文共几卷。名之曰迟川集。见行于世。呜呼。斯集也将久而不敝。后之欲知公者。于此求之。庶乎得其一二。
有馀味。盖蕴蓄明识。形于言语。非人所及。诗亦绝高。世之自负其工者。或莫能彷佛。由此论之。向所谓考观其事业文章。可以见其人之所存者。在公为何如也。公之诗文共几卷。名之曰迟川集。见行于世。呜呼。斯集也将久而不敝。后之欲知公者。于此求之。庶乎得其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