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x 页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序(五首)
序(五首)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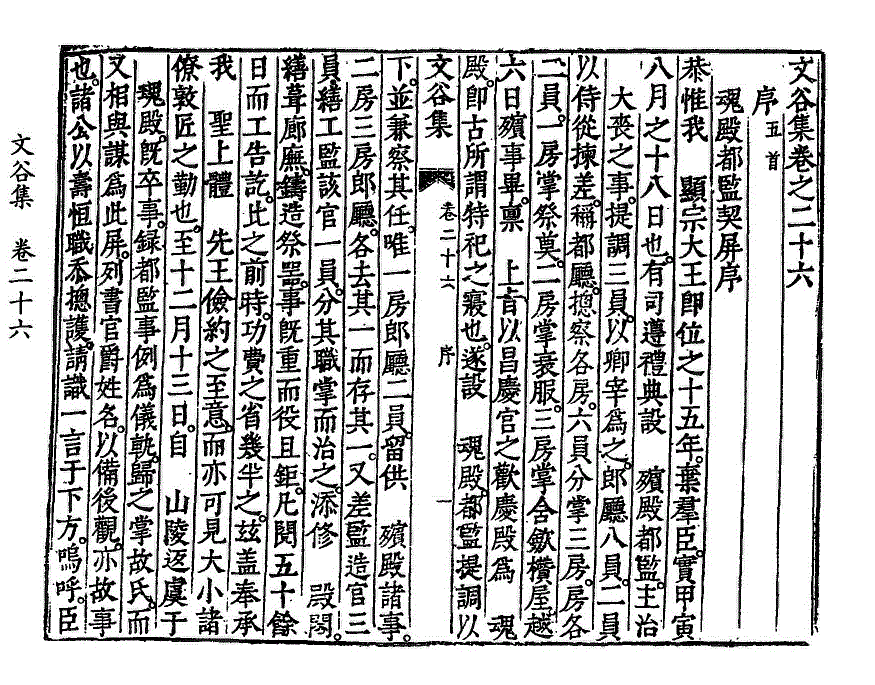 魂殿都监契屏序
魂殿都监契屏序恭惟我 显宗大王即位之十五年。弃群臣。实甲寅八月之十八日也。有司遵礼典设 殡殿都监。主治 大丧之事。提调三员。以卿宰为之。郎厅八员。二员以侍从拣差。称都厅。总察各房。六员分掌三房。房各二员。一房掌祭奠。二房掌衰服。三房掌含敛攒屋。越六日殡事毕。禀 上旨以昌庆宫之欢庆殿为 魂殿。即古所谓特祀之寝也。遂设 魂殿。都监提调以下。并兼察其任。唯一房郎厅二员。留供 殡殿诸事。二房三房郎厅。各去其一而存其一。又差监造官三员,缮工监该官一员。分其职掌而治之。添修 殿阁。缮葺廊庑。铸造祭器。事既重而役且钜。凡阅五十馀日而工告讫。比之前时。功费之省几半之。玆盖奉承我 圣上体 先王俭约之至意。而亦可见大小诸僚敦匠之勤也。至十二月十三日。自 山陵返虞于 魂殿。既卒事。录都监事例为仪轨。归之掌故氏。而又相与谋为此屏。列书官爵姓名。以备后观。亦故事也。诸公以寿恒职忝总护。请识一言于下方。呜呼。臣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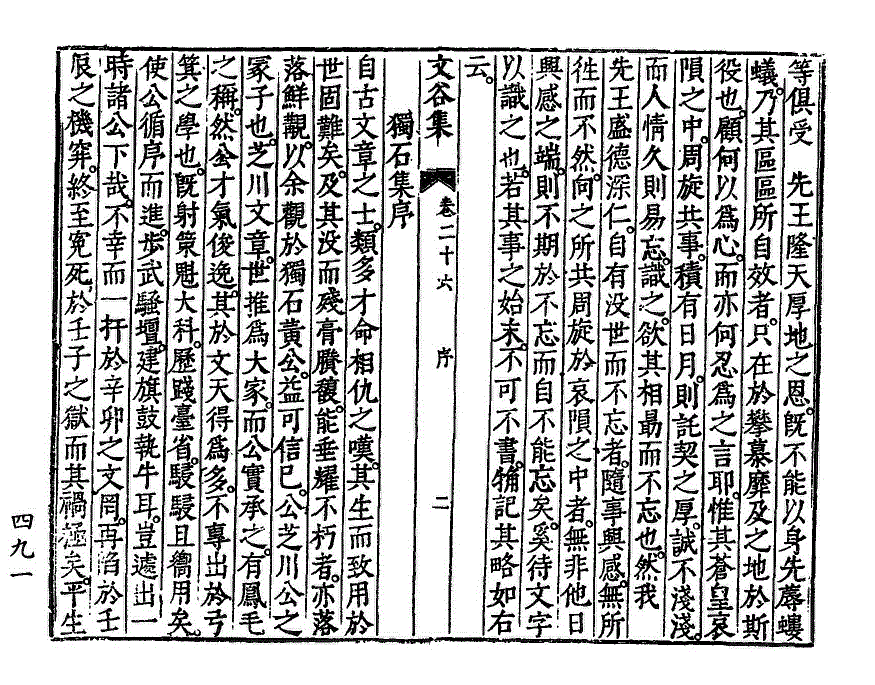 等俱受 先王隆天厚地之恩。既不能以身先蓐蝼蚁。乃其区区所自效者。只在于攀慕靡及之地于斯役也。顾何以为心。而亦何忍为之言耶。惟其苍皇哀陨之中。周旋共事。积有日月。则托契之厚。诚不浅浅。而人情久则易忘。识之。欲其相勖而不忘也。然我 先王盛德深仁。自有没世而不忘者。随事兴感。无所往而不然。向之所共周旋于哀陨之中者。无非他日兴。感之端。则不期于不忘而自不能忘矣。奚待文字以识之也。若其事之始末。不可不书。觕记其略如右云。
等俱受 先王隆天厚地之恩。既不能以身先蓐蝼蚁。乃其区区所自效者。只在于攀慕靡及之地于斯役也。顾何以为心。而亦何忍为之言耶。惟其苍皇哀陨之中。周旋共事。积有日月。则托契之厚。诚不浅浅。而人情久则易忘。识之。欲其相勖而不忘也。然我 先王盛德深仁。自有没世而不忘者。随事兴感。无所往而不然。向之所共周旋于哀陨之中者。无非他日兴。感之端。则不期于不忘而自不能忘矣。奚待文字以识之也。若其事之始末。不可不书。觕记其略如右云。独石集序
自古文章之士。类多才命相仇之叹。其生而致用于世固难矣。及其没而残膏剩馥。能垂耀不朽者。亦落落鲜觏。以余观于独石黄公。益可信已。公芝川公之冢子也。芝川文章。世推为大家。而公实承之。有凤毛之称。然公才气俊逸。其于文天得为多。不专出于弓箕之学也。既射策魁大科。历践台省。骎骎且向用矣。使公循序而进。步武骚坛。建旗鼓执牛耳。岂遽出一时诸公下哉。不幸而一捍于辛卯之文罔。再陷于壬辰之机阱。终至冤死于壬子之狱而其祸极矣。平生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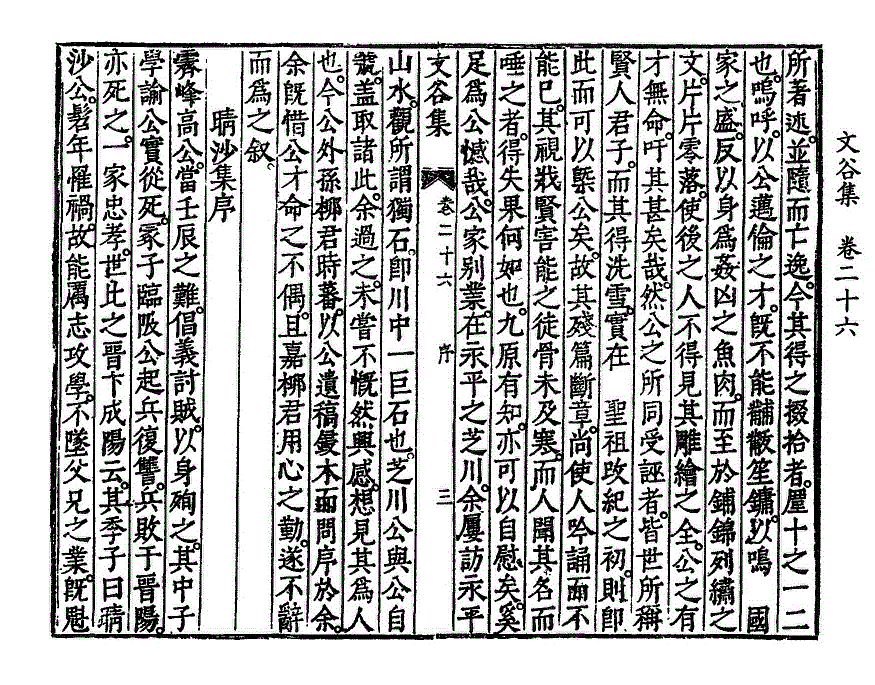 所著述。并随而亡逸。今其得之掇拾者。廑十之一二也。呜呼。以公迈伦之才。既不能黼黻笙镛。以鸣 国家之盛。反以身为奸凶之鱼肉。而至于铺锦列绣之文。片片零落。使后之人不得见其雕绘之全。公之有才无命。吁其甚矣哉。然公之所同受诬者。皆世所称贤人君子。而其得洗雪。实在 圣祖改纪之初。则即此而可以槩公矣。故其残篇断章。尚使人吟诵而不能已。其视戕贤害能之徒骨未及寒。而人闻其名而唾之者。得失果何如也。九原有知。亦可以自慰矣。奚足为公憾哉。公家别业。在永平之芝川。余屡访永平山水。观所谓独石。即川中一巨石也。芝川公与公自号。盖取诸此。余过之。未尝不慨然兴感。想见其为人也。今公外孙柳君时蕃。以公遗稿锓木而问序于余。余既惜公才命之不偶。且嘉柳君用心之勤。遂不辞而为之叙。
所著述。并随而亡逸。今其得之掇拾者。廑十之一二也。呜呼。以公迈伦之才。既不能黼黻笙镛。以鸣 国家之盛。反以身为奸凶之鱼肉。而至于铺锦列绣之文。片片零落。使后之人不得见其雕绘之全。公之有才无命。吁其甚矣哉。然公之所同受诬者。皆世所称贤人君子。而其得洗雪。实在 圣祖改纪之初。则即此而可以槩公矣。故其残篇断章。尚使人吟诵而不能已。其视戕贤害能之徒骨未及寒。而人闻其名而唾之者。得失果何如也。九原有知。亦可以自慰矣。奚足为公憾哉。公家别业。在永平之芝川。余屡访永平山水。观所谓独石。即川中一巨石也。芝川公与公自号。盖取诸此。余过之。未尝不慨然兴感。想见其为人也。今公外孙柳君时蕃。以公遗稿锓木而问序于余。余既惜公才命之不偶。且嘉柳君用心之勤。遂不辞而为之叙。晴沙集序
霁峰高公。当壬辰之难。倡义讨贼。以身殉之。其中子学谕公实从死。冢子临陂公起兵复雠。兵败于晋阳。亦死之。一家忠孝。世比之晋卞成阳云。其季子曰晴沙公。髫年罹祸。故能厉志攻学。不坠父兄之业。既魁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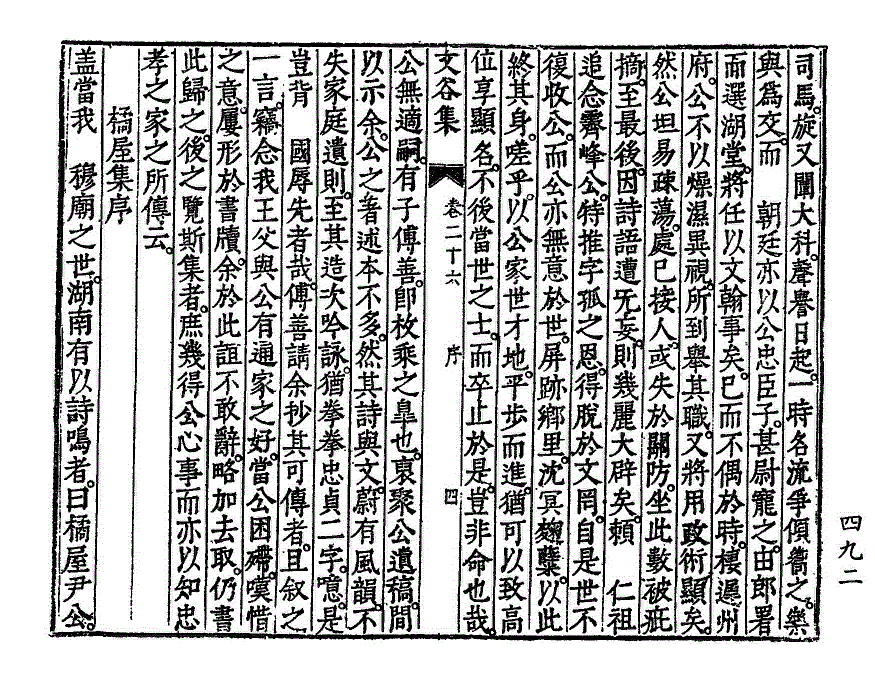 司马。旋又阐大科。声誉日起。一时名流争倾向之。乐与为交。而 朝廷亦以公忠臣子。甚尉宠之。由郎署而选湖堂。将任以文翰事矣。已而不偶于时。栖迟州府。公不以燥湿异视。所到举其职。又将用政术显矣。然公坦易疏荡。处己接人。或失于关防。坐此数被疵摘。至最后。因诗语遭无妄。则几丽大辟矣。赖 仁祖追念霁峰公。特推字孤之恩。得脱于文罔。自是世不复收公。而公亦无意于世。屏迹乡里。沈冥曲蘖。以此终其身。嗟乎。以公家世才地。平步而进。犹可以致高位享显名。不后当世之士。而卒止于是。岂非命也哉。公无适嗣。有子傅善。即枚乘之皋也。裒聚公遗稿。间以示余。公之著述本不多。然其诗与文。蔚有风韵。不失家庭遗则。至其造次吟咏。犹拳拳忠贞二字。噫。是岂背 国辱先者哉。傅善请余抄其可传者。且叙之一言。窃念我王父与公有通家之好。当公困殢。叹惜之意。屡形于书牍。余于此谊不敢辞。略加去取。仍书此归之。后之览斯集者。庶几得公心事而亦以知忠孝之家之所传云。
司马。旋又阐大科。声誉日起。一时名流争倾向之。乐与为交。而 朝廷亦以公忠臣子。甚尉宠之。由郎署而选湖堂。将任以文翰事矣。已而不偶于时。栖迟州府。公不以燥湿异视。所到举其职。又将用政术显矣。然公坦易疏荡。处己接人。或失于关防。坐此数被疵摘。至最后。因诗语遭无妄。则几丽大辟矣。赖 仁祖追念霁峰公。特推字孤之恩。得脱于文罔。自是世不复收公。而公亦无意于世。屏迹乡里。沈冥曲蘖。以此终其身。嗟乎。以公家世才地。平步而进。犹可以致高位享显名。不后当世之士。而卒止于是。岂非命也哉。公无适嗣。有子傅善。即枚乘之皋也。裒聚公遗稿。间以示余。公之著述本不多。然其诗与文。蔚有风韵。不失家庭遗则。至其造次吟咏。犹拳拳忠贞二字。噫。是岂背 国辱先者哉。傅善请余抄其可传者。且叙之一言。窃念我王父与公有通家之好。当公困殢。叹惜之意。屡形于书牍。余于此谊不敢辞。略加去取。仍书此归之。后之览斯集者。庶几得公心事而亦以知忠孝之家之所传云。橘屋集序
盖当我 穆庙之世。湖南有以诗鸣者。曰橘屋尹公。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3H 页
 同时词苑诸公。靡不推许。而我王父文正公与之游从最熟。不佞幼侍家庭。从书箧故纸中。得公与王父酬唱若而篇而读之。恨无由睹其全也。今适御魅于朗州。朗于公旧居海南比壤也。公之曾孙仁厚,天厚兄弟袖公遗稿来视。仍请删定而弁以文。是则不佞乌敢当。窃自幸其宿心之副也。遂受而卒业。则其诗格鍊而调清。咏物写事。无非本乎性情之正。宜其以此鸣于世也。其馀杂著诸文。亦皆赡畅有理趣。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公少学于重峰赵先生。坐此摈于时论。晚又厄于昏朝。蹭蹬下位。而犹秉正不挠。退居乡里。绕屋树橘。自放于酒赋以终其身。一时侪流之所推许。不颛在诗也。公甚有内行。观其所述继母行录。则可知母之所以爱公与公之善事母者。皆非今人所能及。然则公之可传。又岂独诗哉。噫。近世所称词人文士其所著述。能使木灾而纸贵者。其人与文。岂尽有瘉于公哉。独公后承凋残。又未有青云之士为之后焉者。使其隹篇秀句。零落于尘埋蠹食之中。而不得托剞劂以图不朽之传。吁其可惜也已。顾不佞非玄晏无能为三都家役。而重违尹君兄弟之请。且念先故之谊。玆用不揆僭妄。略为之标选。并叙一言
同时词苑诸公。靡不推许。而我王父文正公与之游从最熟。不佞幼侍家庭。从书箧故纸中。得公与王父酬唱若而篇而读之。恨无由睹其全也。今适御魅于朗州。朗于公旧居海南比壤也。公之曾孙仁厚,天厚兄弟袖公遗稿来视。仍请删定而弁以文。是则不佞乌敢当。窃自幸其宿心之副也。遂受而卒业。则其诗格鍊而调清。咏物写事。无非本乎性情之正。宜其以此鸣于世也。其馀杂著诸文。亦皆赡畅有理趣。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公少学于重峰赵先生。坐此摈于时论。晚又厄于昏朝。蹭蹬下位。而犹秉正不挠。退居乡里。绕屋树橘。自放于酒赋以终其身。一时侪流之所推许。不颛在诗也。公甚有内行。观其所述继母行录。则可知母之所以爱公与公之善事母者。皆非今人所能及。然则公之可传。又岂独诗哉。噫。近世所称词人文士其所著述。能使木灾而纸贵者。其人与文。岂尽有瘉于公哉。独公后承凋残。又未有青云之士为之后焉者。使其隹篇秀句。零落于尘埋蠹食之中。而不得托剞劂以图不朽之传。吁其可惜也已。顾不佞非玄晏无能为三都家役。而重违尹君兄弟之请。且念先故之谊。玆用不揆僭妄。略为之标选。并叙一言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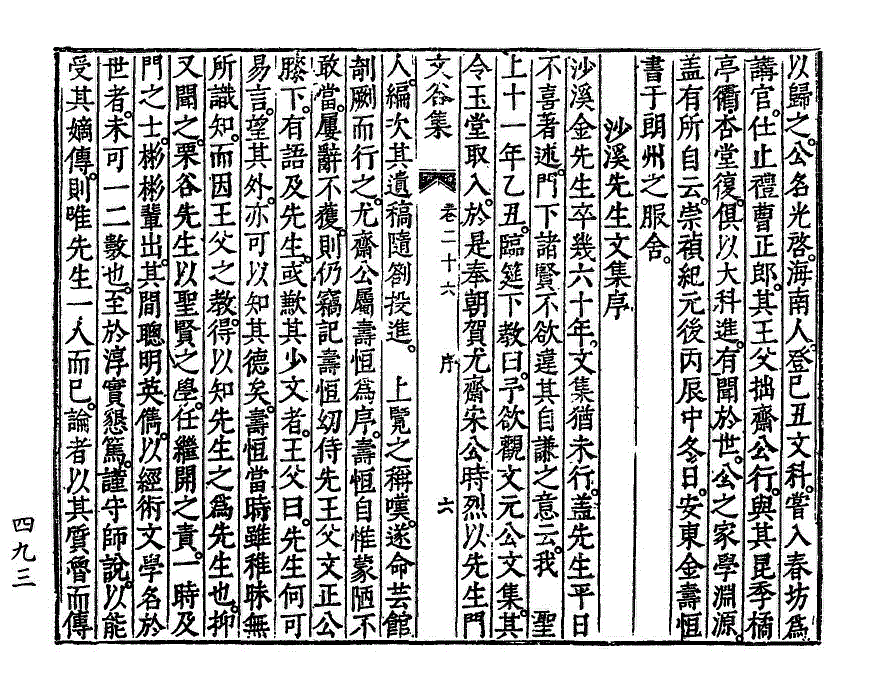 以归之。公名光启。海南人。登己丑文科。尝入春坊为讲官。仕止礼曹正郎。其王父拙斋公行。与其昆季橘亭衢,杏堂复。俱以大科进。有闻于世。公之家学渊源。盖有所自云。崇祯纪元后丙辰中冬日。安东金寿恒书于朗州之服舍。
以归之。公名光启。海南人。登己丑文科。尝入春坊为讲官。仕止礼曹正郎。其王父拙斋公行。与其昆季橘亭衢,杏堂复。俱以大科进。有闻于世。公之家学渊源。盖有所自云。崇祯纪元后丙辰中冬日。安东金寿恒书于朗州之服舍。沙溪先生文集序
沙溪金先生卒几六十年。文集犹未行。盖先生平日不喜著述。门下诸贤不欲违其自谦之意云。我 圣上十一年乙丑。临筵下教曰。予欲观文元公文集。其令玉堂取入。于是奉朝贺尤斋宋公时烈以先生门人。编次其遗稿随劄投进。 上览之称叹。遂命芸馆剞劂而行之。尤斋公属寿恒为序。寿恒自惟蒙陋不敢当。屡辞不获。则仍窃记寿恒幼侍先王父文正公膝下。有语及先生。或歉其少文者。王父曰。先生何可易言。望其外。亦可以知其德矣。寿恒当时虽稚昧无所识知。而因王父之教。得以知先生之为先生也。抑又闻之。栗谷先生以圣贤之学。任继开之责。一时及门之士。彬彬辈出。其间聪明英俊。以经术文学名于世者。未可一二数也。至于淳实恳笃。谨守师说。以能受其嫡传。则唯先生一人而已。论者以其质鲁而传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4H 页
 道。犹曾氏之于孔门。斯诚知言哉。然质鲁之人。世固多有。则谓先生传道。只在于此。而不求其所以传之之实。非知先生者也。夫圣门旨诀。不过曰博文约礼二者。废其一则非学也。先生天赋浑粹。自然近道。而至其问学。则加以人一己百之功。剖析精微。毫釐必谨。克治诚切。老而不懈。又专精礼学。讲讨而服行之。使天叙天秩大明于吾东。其功益伟矣。世皆知先生之能约以礼。而若其博学于文则鲜克知之矣。凡先生之格致思辨。诗书雅言。无非文者。何必摛华藻工笔札而后。谓之文哉。故其发为文字者。虽朴茂简质。无所修饰。而率皆义理明白。体用具备。无一字一句或涉于偏驳浮誇。信乎其为仁义之人之言也。先生所以得斯道之传者。其在斯欤。彼以少文为歉者。岂非浅之为知先生哉。方今世衰道微。为学者不沦于卑陋。则必趋于浮靡。其不为胡广之中庸鹦鹉之能言者几希。我 圣上兴思九原。命刊遗书。欲以嘉惠后学者。其意岂偶然哉。诚使读是集者。精思实践。不务空言。有以默契乎先生传道之实。则溯洛闽达洙泗。由此可致。而庶不负 圣上表章之盛意矣。是集之行也。先生曾孙光城公兄弟考校订正。实相编摩
道。犹曾氏之于孔门。斯诚知言哉。然质鲁之人。世固多有。则谓先生传道。只在于此。而不求其所以传之之实。非知先生者也。夫圣门旨诀。不过曰博文约礼二者。废其一则非学也。先生天赋浑粹。自然近道。而至其问学。则加以人一己百之功。剖析精微。毫釐必谨。克治诚切。老而不懈。又专精礼学。讲讨而服行之。使天叙天秩大明于吾东。其功益伟矣。世皆知先生之能约以礼。而若其博学于文则鲜克知之矣。凡先生之格致思辨。诗书雅言。无非文者。何必摛华藻工笔札而后。谓之文哉。故其发为文字者。虽朴茂简质。无所修饰。而率皆义理明白。体用具备。无一字一句或涉于偏驳浮誇。信乎其为仁义之人之言也。先生所以得斯道之传者。其在斯欤。彼以少文为歉者。岂非浅之为知先生哉。方今世衰道微。为学者不沦于卑陋。则必趋于浮靡。其不为胡广之中庸鹦鹉之能言者几希。我 圣上兴思九原。命刊遗书。欲以嘉惠后学者。其意岂偶然哉。诚使读是集者。精思实践。不务空言。有以默契乎先生传道之实。则溯洛闽达洙泗。由此可致。而庶不负 圣上表章之盛意矣。是集之行也。先生曾孙光城公兄弟考校订正。实相编摩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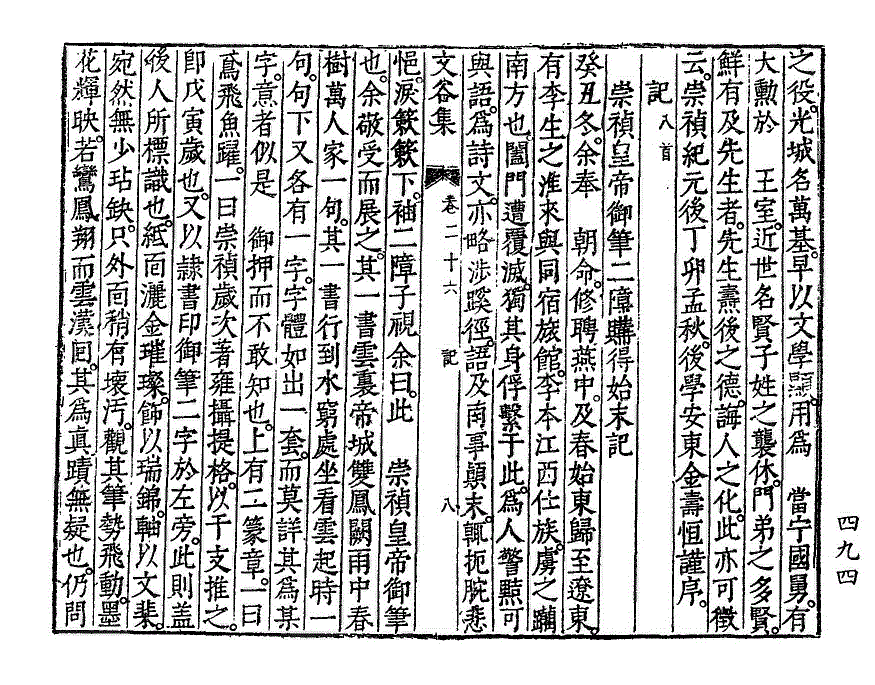 之役。光城名万基。早以文学显。用为 当宁国舅。有大勋于 王室。近世名贤子姓之袭休。门弟之多贤。鲜有及先生者。先生焘后之德。诲人之化。此亦可徵云。崇祯纪元后丁卯孟秋。后学安东金寿恒谨序。
之役。光城名万基。早以文学显。用为 当宁国舅。有大勋于 王室。近世名贤子姓之袭休。门弟之多贤。鲜有及先生者。先生焘后之德。诲人之化。此亦可徵云。崇祯纪元后丁卯孟秋。后学安东金寿恒谨序。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记(八首)
崇祯皇帝御笔二障购得始末记
癸丑冬。余奉 朝命。修聘燕中。及春始东归至辽东。有李生之淮来与同宿旅馆。李本江西仕族。虏之躏南方也。阖门遭覆灭。独其身俘系于此。为人警黠可与语。为诗文。亦略涉蹊径。语及南事颠末。辄扼腕悲悒。泪簌簌下。袖二障子视余曰。此 崇祯皇帝御笔也。余敬受而展之。其一。书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一句。其一。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句。句下又各有一字。字体如出一套。而莫详其为某字。意者似是 御押而不敢知也。上有二篆章。一曰鸢飞鱼跃。一曰崇祯岁次著雍摄提格。以干支推之。即戊寅岁也。又以隶书印御笔二字于左旁。此则盖后人所标识也。纸面洒金璀璨。饰以瑞锦。轴以文棐。宛然无少玷缺。只外面稍有坏污。观其笔势飞动。墨花辉映。若鸾凤翔而云汉回。其为真迹无疑也。仍问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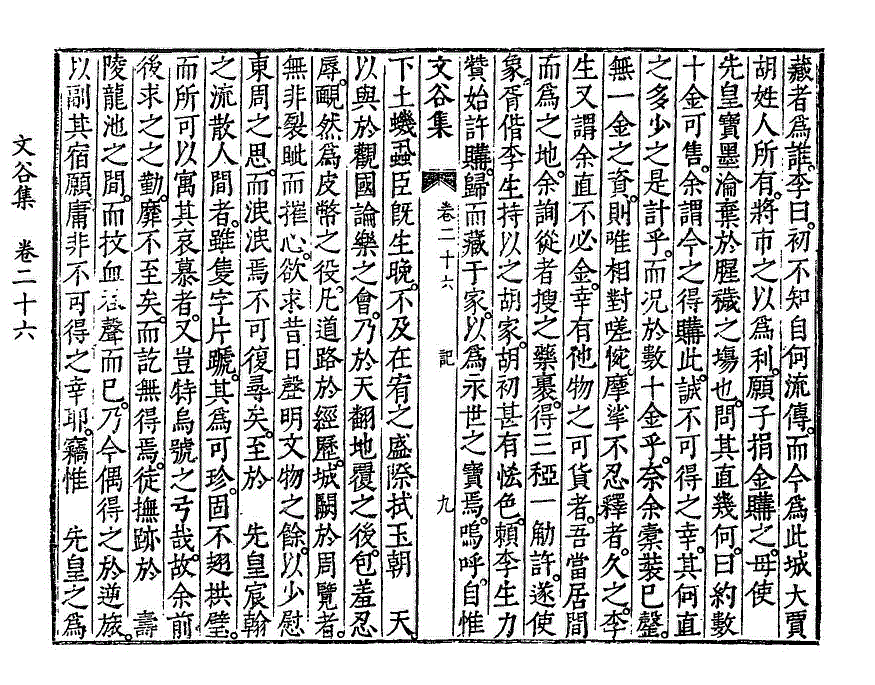 藏者为谁。李曰。初不知自何流传。而今为此城大贾胡姓人所有。将市之以为利。愿子捐金购之。毋使 先皇宝墨沦弃于腥秽之场也。问其直几何。曰约数十金可售。余谓今之得购此。诚不可得之幸。其何直之多少之是计乎。而况于数十金乎。奈余橐装已罄。无一金之资。则唯相对嗟惋。摩挲不忍释者。久之。李生又谓余直不必金。幸有他物之可货者。吾当居间而为之地。余询从者搜之药裹。得三稏一觔许。遂使象。胥偕李生持以之胡家。胡初甚有吝色。赖李生力赞始许购。归而藏于家。以为永世之宝焉。呜呼。自惟下土虮虱。臣既生晚。不及在宥之盛际。拭玉朝 天。以与于观国论乐之会。乃于天翻地覆之后。包羞忍辱。腼然为皮币之役。凡道路于经历。城阙于周览者。无非裂眦而摧心。欲求昔日声明文物之馀。以少慰东周之思。而泯泯焉不可复寻矣。至于 先皇宸翰之流散人间者。虽只字片蹄。其为可珍。固不翅拱璧。而所可以寓其哀慕者。又岂特乌号之弓哉。故余前后求之之勤。靡不至矣。而讫无得焉。徒抚迹于 寿陵龙池之间。而抆血吞声而已。乃今偶得之于逆旅。以副其宿愿。庸非不可得之幸耶。窃惟 先皇之为
藏者为谁。李曰。初不知自何流传。而今为此城大贾胡姓人所有。将市之以为利。愿子捐金购之。毋使 先皇宝墨沦弃于腥秽之场也。问其直几何。曰约数十金可售。余谓今之得购此。诚不可得之幸。其何直之多少之是计乎。而况于数十金乎。奈余橐装已罄。无一金之资。则唯相对嗟惋。摩挲不忍释者。久之。李生又谓余直不必金。幸有他物之可货者。吾当居间而为之地。余询从者搜之药裹。得三稏一觔许。遂使象。胥偕李生持以之胡家。胡初甚有吝色。赖李生力赞始许购。归而藏于家。以为永世之宝焉。呜呼。自惟下土虮虱。臣既生晚。不及在宥之盛际。拭玉朝 天。以与于观国论乐之会。乃于天翻地覆之后。包羞忍辱。腼然为皮币之役。凡道路于经历。城阙于周览者。无非裂眦而摧心。欲求昔日声明文物之馀。以少慰东周之思。而泯泯焉不可复寻矣。至于 先皇宸翰之流散人间者。虽只字片蹄。其为可珍。固不翅拱璧。而所可以寓其哀慕者。又岂特乌号之弓哉。故余前后求之之勤。靡不至矣。而讫无得焉。徒抚迹于 寿陵龙池之间。而抆血吞声而已。乃今偶得之于逆旅。以副其宿愿。庸非不可得之幸耶。窃惟 先皇之为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5L 页
 此书在戊寅。而越六年而有甲申之祸。甲申之去今未及三纪。则岁月非久远也。以 先皇天纵之能。挥洒于清燕之暇者。必有充溢于宝文宸奎之藏。未可以遽数也。然而至于今日。求之勤而得之难如此。则可见其传于世者之至鲜也。独此二障阅几兵燹。而能保完如旧。斯已奇矣。其不为昭陵玉匣之殉。而落于一贾胡之手。埋没于毡庐野肆之中。固可谓不幸。而尘沙之所蒙翳。蠹鼠之所侵蚀。不遂至于隳失者。亦幸矣。一朝而因其图利之心。终归于勤求不得之贱臣。得以誇耀海域以永其传。玆又岂非幸之幸也。虽然。此岂容人力哉。非有鬼物阴护而潜卫。则尚可以得此乎哉。噫亦异矣。抑余因此而重有感焉。国君死社稷。古今之通谊也。废兴存亡。有国之所不免。而历选终古。能蹈此义者。蔑蔑乎无闻焉。惟我 先皇帝当苍皇颠覆之际。身与宗社俱亡。其巍巍义烈。度越百王。真可谓无愧于 祖宗而有辞于天下后世矣。此固 中朝臣子极天之至痛。而使天下后世之人闻之。亦可为掩泣而气塞。况我东土被 皇家子视之泽。出寻常万万者哉。道路城阙之所历览。犹为之兴哀。况此 御笔二十四字一句一点。皆出于心
此书在戊寅。而越六年而有甲申之祸。甲申之去今未及三纪。则岁月非久远也。以 先皇天纵之能。挥洒于清燕之暇者。必有充溢于宝文宸奎之藏。未可以遽数也。然而至于今日。求之勤而得之难如此。则可见其传于世者之至鲜也。独此二障阅几兵燹。而能保完如旧。斯已奇矣。其不为昭陵玉匣之殉。而落于一贾胡之手。埋没于毡庐野肆之中。固可谓不幸。而尘沙之所蒙翳。蠹鼠之所侵蚀。不遂至于隳失者。亦幸矣。一朝而因其图利之心。终归于勤求不得之贱臣。得以誇耀海域以永其传。玆又岂非幸之幸也。虽然。此岂容人力哉。非有鬼物阴护而潜卫。则尚可以得此乎哉。噫亦异矣。抑余因此而重有感焉。国君死社稷。古今之通谊也。废兴存亡。有国之所不免。而历选终古。能蹈此义者。蔑蔑乎无闻焉。惟我 先皇帝当苍皇颠覆之际。身与宗社俱亡。其巍巍义烈。度越百王。真可谓无愧于 祖宗而有辞于天下后世矣。此固 中朝臣子极天之至痛。而使天下后世之人闻之。亦可为掩泣而气塞。况我东土被 皇家子视之泽。出寻常万万者哉。道路城阙之所历览。犹为之兴哀。况此 御笔二十四字一句一点。皆出于心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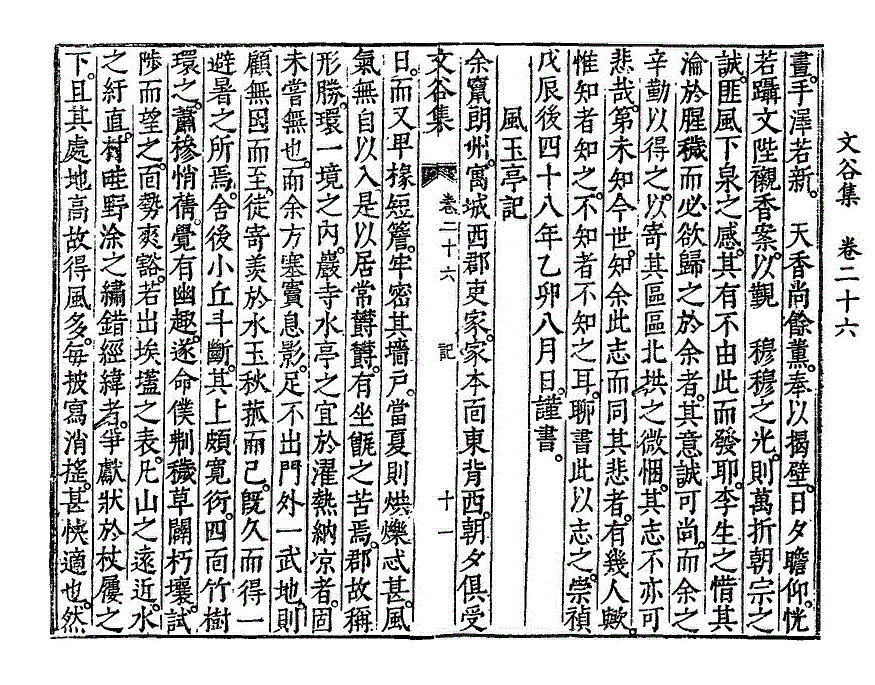 画。手泽若新。 天香尚馀薰。奉以揭壁。日夕瞻仰。恍若蹑文陛衬香案。以觐 穆穆之光。则万折朝宗之诚。匪风下泉之感。其有不由此而发耶。李生之惜其沦于腥秽而必欲归之于余者。其意诚可尚。而余之辛勤以得之。以寄其区区北拱之微悃。其志不亦可悲哉。第未知今世。知余此志而同其悲者。有几人欤。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之耳。聊书此以志之。崇祯戊辰后四十八年乙卯八月日。谨书。
画。手泽若新。 天香尚馀薰。奉以揭壁。日夕瞻仰。恍若蹑文陛衬香案。以觐 穆穆之光。则万折朝宗之诚。匪风下泉之感。其有不由此而发耶。李生之惜其沦于腥秽而必欲归之于余者。其意诚可尚。而余之辛勤以得之。以寄其区区北拱之微悃。其志不亦可悲哉。第未知今世。知余此志而同其悲者。有几人欤。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之耳。聊书此以志之。崇祯戊辰后四十八年乙卯八月日。谨书。风玉亭记
余窜朗州。寓城西郡吏家。家本面东背西。朝夕俱受日。而又卑椽短檐。牢密其墙户。当夏则烘烁忒甚。风气无自以入。是以居常郁郁。有坐甑之苦焉。郡故称形胜。环一境之内。岩寺水亭之宜于濯热纳凉者。固未尝无也。而余方塞窦息影。足不出门外一武地。则顾无因而至。徒寄羡于水玉秋菰而已。既久而得一避暑之所焉。舍后小丘斗断。其上颇宽衍。四面竹树环之。萧椮悄茜。觉有幽趣。遂命仆刜秽草辟朽壤。试陟而望之。面势爽豁。若出埃壒之表。凡山之远近。水之纡直。村畦野涂之绣错经纬者。争献状于杖屦之下。且其处地高故得风多。每披写消摇。甚快适也。然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6L 页
 暴阳凌雨。不可以恒处。则谋所以庇之者。而鸠材营宇。非唯力诎。亦非余所欲也。乃取巨竹构一架为亭。杗桷栟杙。皆以竹为之。不杂一木。独其下以木设为方机。穴其四隅而承其柱。欲其朴属而毋使土侵竹也。其高一寻有半。其广如之。其脩不及高一尺。不崇朝而工已讫。以蓬席盖其顶。编栅布其底以代床。上施以簟。簟与栅亦竹也。亭既成。余乃葛巾布褐。日相羊其中。呻书咏诗以自乐。其所乐而倦。则引觞而醉。据几而眠。熙熙然与造物者游。既觉而起则鲜飙自生。翠叶交荫。月岳爽气依依入襟袖。令人神清心旷。有驭泠风羾寒门意。以至暮色苍然。新月映林梢。而兴犹未阑也。当是时也。忽不知身之为僇人,地之为荒裔。时之为炎夏。则况世之是非。得丧荣辱。复有可以撄吾怀者耶。假使余得致身于向所谓岩寺水亭者。而其清旷自适之趣。未必能若是也。昔柳柳州记钴鉧潭云。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玆潭欤。今余之乐于斯而忘其困者。亦玆亭之助也。则乌可使没没无名。遂名之曰风玉。客有过而难余者曰。风者亭之所固有。名之宜矣。然其结构觕朴。不过稍饰于橧巢林樾者耳。强名之为亭。亦云不称。今乃揭玉为名。
暴阳凌雨。不可以恒处。则谋所以庇之者。而鸠材营宇。非唯力诎。亦非余所欲也。乃取巨竹构一架为亭。杗桷栟杙。皆以竹为之。不杂一木。独其下以木设为方机。穴其四隅而承其柱。欲其朴属而毋使土侵竹也。其高一寻有半。其广如之。其脩不及高一尺。不崇朝而工已讫。以蓬席盖其顶。编栅布其底以代床。上施以簟。簟与栅亦竹也。亭既成。余乃葛巾布褐。日相羊其中。呻书咏诗以自乐。其所乐而倦。则引觞而醉。据几而眠。熙熙然与造物者游。既觉而起则鲜飙自生。翠叶交荫。月岳爽气依依入襟袖。令人神清心旷。有驭泠风羾寒门意。以至暮色苍然。新月映林梢。而兴犹未阑也。当是时也。忽不知身之为僇人,地之为荒裔。时之为炎夏。则况世之是非。得丧荣辱。复有可以撄吾怀者耶。假使余得致身于向所谓岩寺水亭者。而其清旷自适之趣。未必能若是也。昔柳柳州记钴鉧潭云。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玆潭欤。今余之乐于斯而忘其困者。亦玆亭之助也。则乌可使没没无名。遂名之曰风玉。客有过而难余者曰。风者亭之所固有。名之宜矣。然其结构觕朴。不过稍饰于橧巢林樾者耳。强名之为亭。亦云不称。今乃揭玉为名。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7H 页
 有若侈大者然。其意何居。余应曰否否。余性素爱竹。幸今得处于万竹之中。而又以竹为亭。其起居枕藉偃仰顾眄。无非竹也。夫风之与竹最相宜。观于程夫子感应之说。亦可知矣。每风之来触于亭也。磨飐戛击。自相成声。琮琤乎铿锵乎。若碎琳琅而鸣玦环。非亭之能声也。竹为之声也。又四顾而听之。则竹之林立于左右者。无不为风所摇。玱玱珊珊。其声清越以长。非竹之能声也。风为之声也。声虽风与竹之为。而其听于耳则无非玉也。名亭以玉。奚不可之有。且也古之君子比德于玉。而其泽栗廉垂之德。竹实似之。故比玉于竹者亦多矣。此淇澚绿竹之咏。所以兴琢磨圭璧之盛德也。余之于竹。不徒挹其风之清以涤其烦歊。亦将取其德之比玉者。以为进修之则。则以玉名亭。意实在斯。觕朴非所嫌也。至若侈大之云。不亦浅之知我哉。客唯唯而退。因书其语以为记。
有若侈大者然。其意何居。余应曰否否。余性素爱竹。幸今得处于万竹之中。而又以竹为亭。其起居枕藉偃仰顾眄。无非竹也。夫风之与竹最相宜。观于程夫子感应之说。亦可知矣。每风之来触于亭也。磨飐戛击。自相成声。琮琤乎铿锵乎。若碎琳琅而鸣玦环。非亭之能声也。竹为之声也。又四顾而听之。则竹之林立于左右者。无不为风所摇。玱玱珊珊。其声清越以长。非竹之能声也。风为之声也。声虽风与竹之为。而其听于耳则无非玉也。名亭以玉。奚不可之有。且也古之君子比德于玉。而其泽栗廉垂之德。竹实似之。故比玉于竹者亦多矣。此淇澚绿竹之咏。所以兴琢磨圭璧之盛德也。余之于竹。不徒挹其风之清以涤其烦歊。亦将取其德之比玉者。以为进修之则。则以玉名亭。意实在斯。觕朴非所嫌也。至若侈大之云。不亦浅之知我哉。客唯唯而退。因书其语以为记。安用堂记
昔韩昌黎送李愿归盘谷。述愿之言。历叙遇于世与不遇者之事。虽一归之命。而其趣舍之意可见。至其末。特提奔走徼倖者而断之。则其贤不肖之分。岂不益较然哉。噫。士之遇不遇。各有命焉。固不可以力致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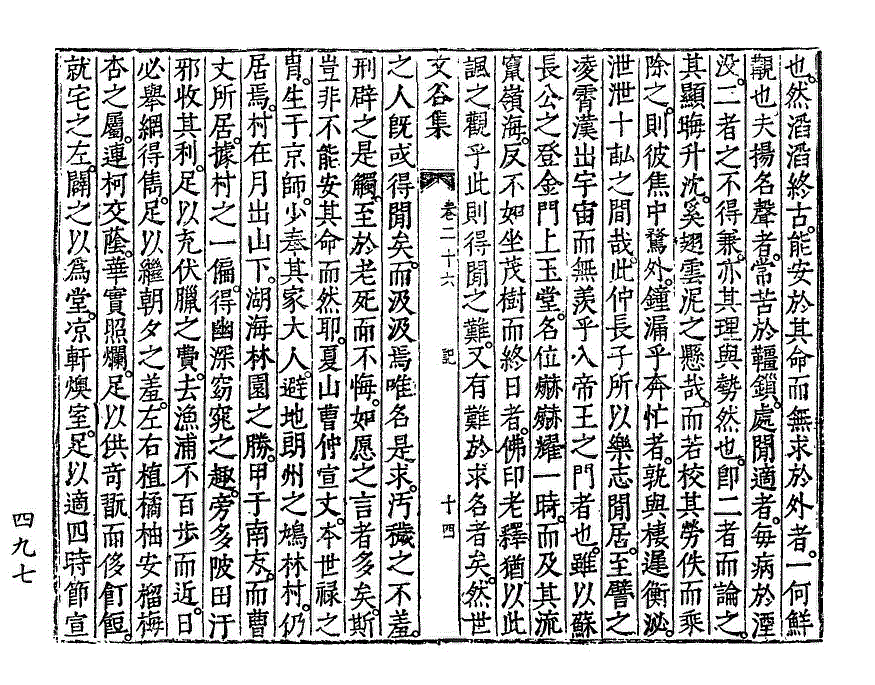 也。然滔滔终古。能安。于其命而无求于外者。一何鲜觏也。夫扬名声者。常苦于缰锁。处閒适者。每病于湮没。二者之不得兼。亦其理与势然也。即二者而论之。其显晦升沈。奚翅云泥之悬哉。而若校其劳佚而乘除之。则彼焦中鹜外。钟漏乎奔忙者。孰与栖迟衡泌。泄泄十亩之间哉。此仲长子所以乐志閒居。至譬之凌霄汉出宇宙而无羡乎入帝王之门者也。虽以苏长公之登金门上玉堂。名位赫赫耀一时。而及其流窜岭海。反不如坐茂树而终日者。佛印老释犹以此讽之。观乎此则得閒之难。又有难于求名者矣。然世之人既或得閒矣。而汲汲焉唯名是求。污秽之不羞。刑辟之是触。至于老死而不悔。如愿之言者多矣。斯岂非不能安其命而然耶。夏山曹仲宣丈。本世禄之胄。生于京师。少奉其家大人。避地朗州之鸠林村。仍居焉。村在月出山下。湖海林园之胜。甲于南友。而曹丈所居。据村之一偏。得幽深窈窕之趣。旁多陂田污邪收其利。足以充伏腊之费。去渔浦不百步而近。日必举网得隽。足以继朝夕之羞。左右植橘柚安榴梅杏之属。连柯交荫。华实照烂。足以供奇玩而侈饤饾。就宅之左。辟之以为堂。凉轩燠室。足以适四时节宣
也。然滔滔终古。能安。于其命而无求于外者。一何鲜觏也。夫扬名声者。常苦于缰锁。处閒适者。每病于湮没。二者之不得兼。亦其理与势然也。即二者而论之。其显晦升沈。奚翅云泥之悬哉。而若校其劳佚而乘除之。则彼焦中鹜外。钟漏乎奔忙者。孰与栖迟衡泌。泄泄十亩之间哉。此仲长子所以乐志閒居。至譬之凌霄汉出宇宙而无羡乎入帝王之门者也。虽以苏长公之登金门上玉堂。名位赫赫耀一时。而及其流窜岭海。反不如坐茂树而终日者。佛印老释犹以此讽之。观乎此则得閒之难。又有难于求名者矣。然世之人既或得閒矣。而汲汲焉唯名是求。污秽之不羞。刑辟之是触。至于老死而不悔。如愿之言者多矣。斯岂非不能安其命而然耶。夏山曹仲宣丈。本世禄之胄。生于京师。少奉其家大人。避地朗州之鸠林村。仍居焉。村在月出山下。湖海林园之胜。甲于南友。而曹丈所居。据村之一偏。得幽深窈窕之趣。旁多陂田污邪收其利。足以充伏腊之费。去渔浦不百步而近。日必举网得隽。足以继朝夕之羞。左右植橘柚安榴梅杏之属。连柯交荫。华实照烂。足以供奇玩而侈饤饾。就宅之左。辟之以为堂。凉轩燠室。足以适四时节宣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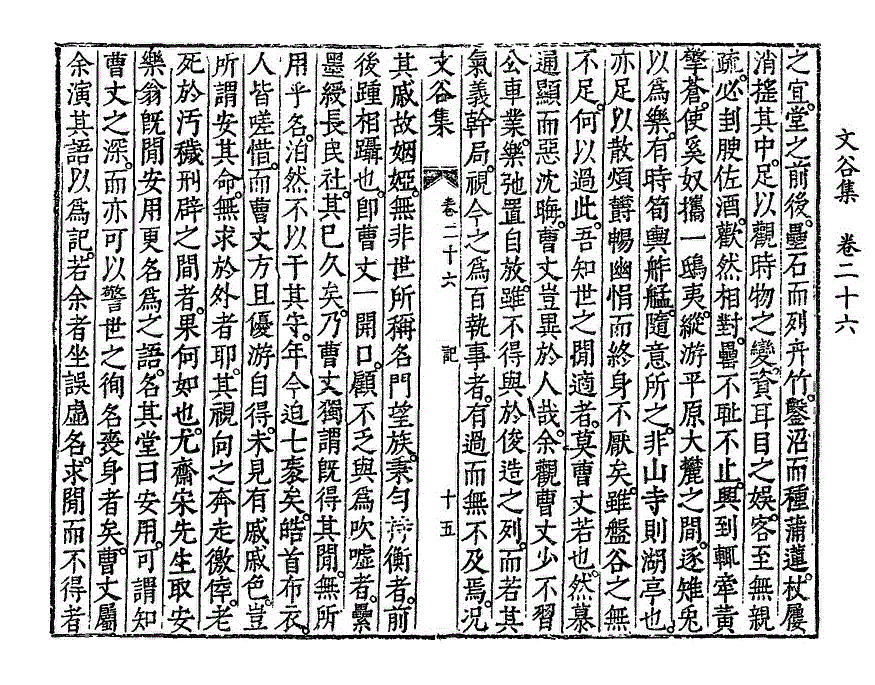 之宜。堂之前后。垒石而列卉竹。凿沼而种蒲莲。杖屦消摇其中。足以观时物之变。资耳目之娱。客至无亲疏。必刲腴佐酒。欢然相对。罍不耻不止。兴到辄牵黄擎苍。使奚奴携一鸱夷。纵游平原大麓之间。逐雉兔以为乐。有时笋舆舴艋。随意所之。非山寺则湖亭也。亦足以散烦郁畅幽悁而终身不厌矣。虽盘谷之无不足。何以过此。吾知世之閒适者。莫曹丈若也。然慕通显而恶沈晦。曹丈岂异于人哉。余观曹丈少不习公车业。乐弛置自放。虽不得与于俊造之列。而若其气义干局。视今之为百执事者。有过而无不及焉。况其戚故姻娅。无非世所称名门望族。秉匀持衡者。前后踵相蹑也。即曹丈一开口。顾不乏与为吹嘘者。累墨绶长民社。其已久矣。乃曹丈独谓既得其閒。无所用乎名。泊然不以干其守。年今迫七帙矣。皓首布衣。人皆嗟惜。而曹丈方且优游自得。未见有戚戚色。岂所谓安其命。无求于外者耶。其视向之奔走徼倖。老死于污秽刑辟之间者。果何如也。尤斋宋先生取安乐翁既閒安用更名为之语。名其堂曰安用。可谓知曹丈之深。而亦可以警世之徇名丧身者矣。曹丈属余演其语以为记。若余者坐误虚名。求閒而不得者
之宜。堂之前后。垒石而列卉竹。凿沼而种蒲莲。杖屦消摇其中。足以观时物之变。资耳目之娱。客至无亲疏。必刲腴佐酒。欢然相对。罍不耻不止。兴到辄牵黄擎苍。使奚奴携一鸱夷。纵游平原大麓之间。逐雉兔以为乐。有时笋舆舴艋。随意所之。非山寺则湖亭也。亦足以散烦郁畅幽悁而终身不厌矣。虽盘谷之无不足。何以过此。吾知世之閒适者。莫曹丈若也。然慕通显而恶沈晦。曹丈岂异于人哉。余观曹丈少不习公车业。乐弛置自放。虽不得与于俊造之列。而若其气义干局。视今之为百执事者。有过而无不及焉。况其戚故姻娅。无非世所称名门望族。秉匀持衡者。前后踵相蹑也。即曹丈一开口。顾不乏与为吹嘘者。累墨绶长民社。其已久矣。乃曹丈独谓既得其閒。无所用乎名。泊然不以干其守。年今迫七帙矣。皓首布衣。人皆嗟惜。而曹丈方且优游自得。未见有戚戚色。岂所谓安其命。无求于外者耶。其视向之奔走徼倖。老死于污秽刑辟之间者。果何如也。尤斋宋先生取安乐翁既閒安用更名为之语。名其堂曰安用。可谓知曹丈之深。而亦可以警世之徇名丧身者矣。曹丈属余演其语以为记。若余者坐误虚名。求閒而不得者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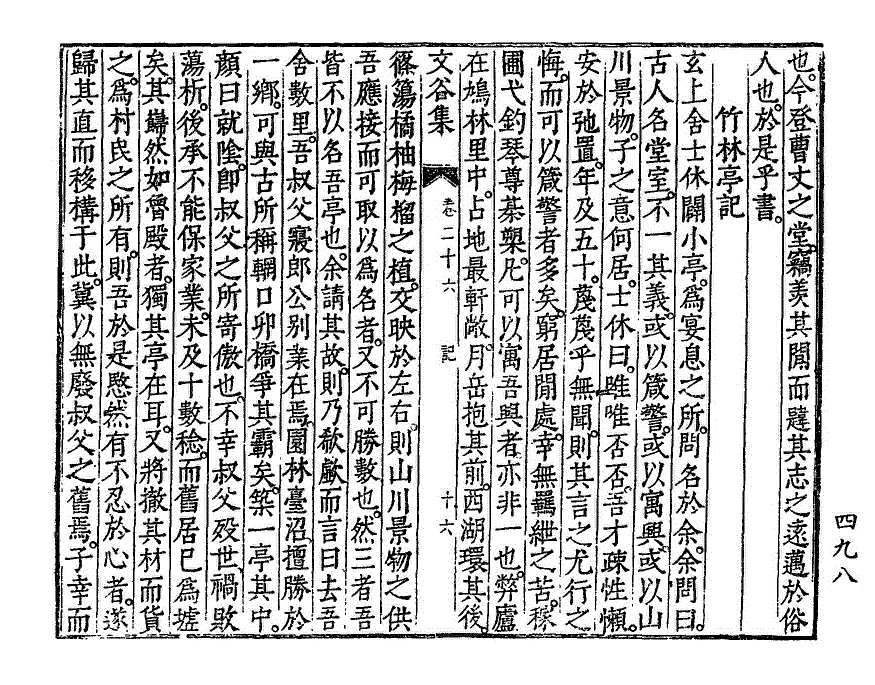 也。今登曹丈之堂。窃羡其閒而韪其志之远迈于俗人也。于是乎书。
也。今登曹丈之堂。窃羡其閒而韪其志之远迈于俗人也。于是乎书。竹林亭记
玄上舍士休辟小亭。为宴息之所。问名于余。余问曰。古人名堂室。不一其义。或以箴警。或以寓兴。或以山川景物。子之意何居。士休曰。唯唯否否。吾才疏性懒。安于弛置。年及五十。蔑蔑乎无闻。则其言之尤行之悔。而可以箴警者多矣。穷居閒处。幸无羁绁之苦。稼圃弋钓琴尊棋槊。凡可以寓吾兴者。亦非一也。弊庐在鸠林里中。占地最轩敞。月岳抱其前。西湖环其后。筱簜橘柚梅榴之植。交映于左右。则山川景物之供吾应接而可取以为名者。又不可胜数也。然三者吾皆不以名吾亭也。余请其故。则乃欷歔而言曰去吾舍数里。吾叔父寝郎公别业在焉。园林台沼。擅胜于一乡。可与古所称辋口卯桥争其霸矣。筑一亭其中。颜曰就阴。即叔父之所寄傲也。不幸叔父殁世。祸败荡析。后承不能保家业。未及十数稔。而旧居已为墟矣。其岿然如鲁殿者。独其亭在耳。又将撤其材而货之。为村民之所有。则吾于是悯然有不忍于心者。遂归其直而移构于此。冀以无废叔父之旧焉。子幸而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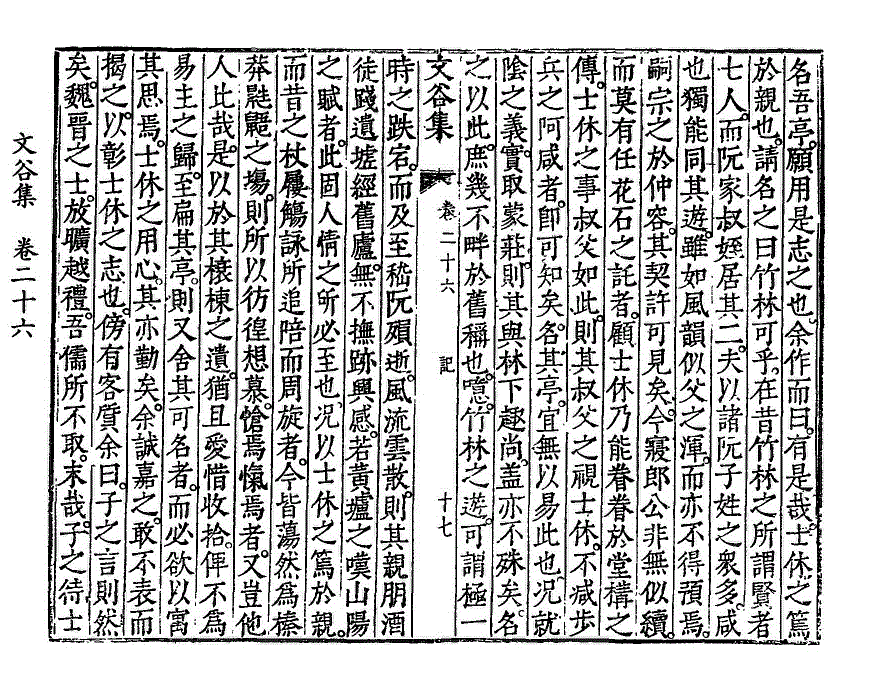 名吾亭。愿用是志之也。余作而曰。有是哉。士休之笃于亲也。请名之曰竹林可乎。在昔竹林之所谓贤者七人。而阮家叔侄居其二。夫以诸阮子姓之众多。咸也独能同其游。虽如风韵似父之浑。而亦不得预焉。嗣宗之于仲容。其契许可见矣。今寝郎公非无似续。而莫有任花石之托者。顾士休乃能眷眷于堂构之传。士休之事叔父如此。则其叔父之视士休。不减步兵之阿咸者。即可知矣。名其亭。宜无以易此也。况就阴之义。实取蒙庄。则其与林下趣尚。盖亦不殊矣。名之以此。庶几不畔于旧称也。噫。竹林之游。可谓极一时之跌宕。而及至嵇阮殒逝。风流云散。则其亲朋酒徒践遗墟经旧庐。无不抚迹兴感。若黄垆之叹山阳之赋者。此固人情之所必至也况以士休之笃于亲。而昔之杖屦觞咏所追陪而周旋者。今皆荡然为榛莽鼪鼯之场。则所以彷徨想慕。怆焉忾焉者。又岂他人比哉。是以于其榱栋之遗。犹且爱惜收拾。俾不为易主之归。至扁其亭。则又舍其可名者。而必欲以寓其思焉。士休之用心。其亦勤矣。余诚嘉之。敢不表而揭之。以彰士休之志也。傍有客质余曰。子之言则然矣。魏晋之士。放旷越礼。吾儒所不取。末哉。子之待士
名吾亭。愿用是志之也。余作而曰。有是哉。士休之笃于亲也。请名之曰竹林可乎。在昔竹林之所谓贤者七人。而阮家叔侄居其二。夫以诸阮子姓之众多。咸也独能同其游。虽如风韵似父之浑。而亦不得预焉。嗣宗之于仲容。其契许可见矣。今寝郎公非无似续。而莫有任花石之托者。顾士休乃能眷眷于堂构之传。士休之事叔父如此。则其叔父之视士休。不减步兵之阿咸者。即可知矣。名其亭。宜无以易此也。况就阴之义。实取蒙庄。则其与林下趣尚。盖亦不殊矣。名之以此。庶几不畔于旧称也。噫。竹林之游。可谓极一时之跌宕。而及至嵇阮殒逝。风流云散。则其亲朋酒徒践遗墟经旧庐。无不抚迹兴感。若黄垆之叹山阳之赋者。此固人情之所必至也况以士休之笃于亲。而昔之杖屦觞咏所追陪而周旋者。今皆荡然为榛莽鼪鼯之场。则所以彷徨想慕。怆焉忾焉者。又岂他人比哉。是以于其榱栋之遗。犹且爱惜收拾。俾不为易主之归。至扁其亭。则又舍其可名者。而必欲以寓其思焉。士休之用心。其亦勤矣。余诚嘉之。敢不表而揭之。以彰士休之志也。傍有客质余曰。子之言则然矣。魏晋之士。放旷越礼。吾儒所不取。末哉。子之待士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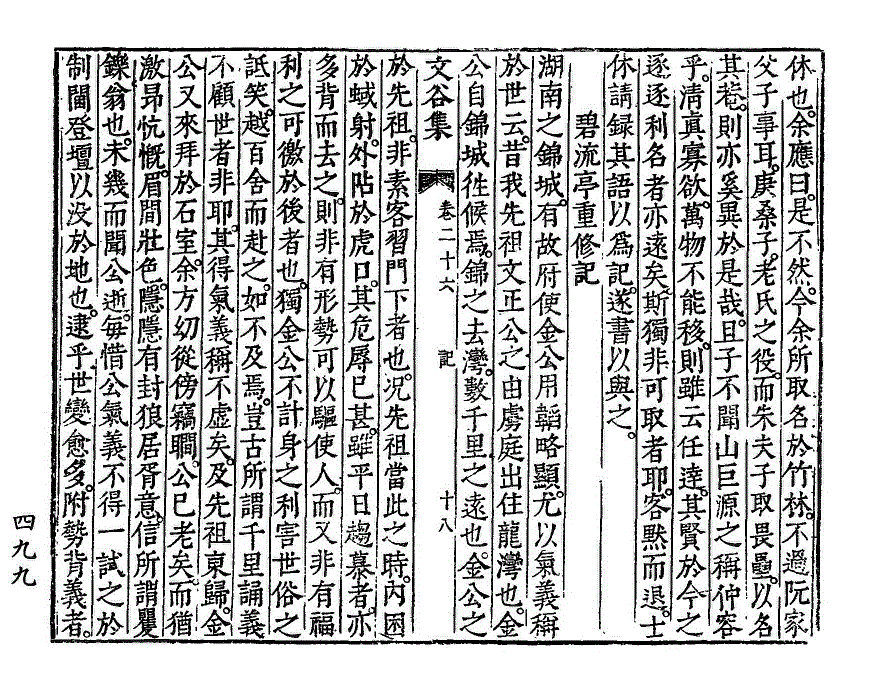 休也。余应曰。是不然。今余所取名于竹林。不过阮家父子事耳。庚桑子。老氏之役。而朱夫子取畏垒。以名其庵。则亦奚异于是哉。且子不闻山巨源之称仲容乎。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则虽云任达。其贤于今之逐逐利名者亦远矣。斯独非可取者耶。客默而退。士休请录其语以为记。遂书以与之。
休也。余应曰。是不然。今余所取名于竹林。不过阮家父子事耳。庚桑子。老氏之役。而朱夫子取畏垒。以名其庵。则亦奚异于是哉。且子不闻山巨源之称仲容乎。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则虽云任达。其贤于今之逐逐利名者亦远矣。斯独非可取者耶。客默而退。士休请录其语以为记。遂书以与之。碧流亭重修记
湖南之锦城。有故府使金公用韬略显。尤以气义称于世云。昔我先祖文正公之由虏庭出住龙湾也。金公自锦城往候焉。锦之去湾。数千里之远也。金公之于先祖。非素客习门下者也。况先祖当此之时。内困于蜮射。外阽于虎口。其危辱已甚。虽平日趋慕者。亦多背而去之。则非有形势可以驱使人。而又非有福利之可徼于后者也。独金公不计身之利害世俗之诋笑。越百舍而赴之。如不及焉。岂古所谓千里诵义不顾世者非耶。其得气义称不虚矣。及先祖东归。金公又来拜于石室。余方幼从傍窃瞯。公已老矣。而犹激昂忼慨。眉间壮色。隐隐有封狼居胥意。信所谓矍铄翁也。未几而闻公逝。每惜公气义不得一试之于制阃登坛以没于地也。逮乎世变愈多。附势背义者。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0H 页
 滔滔皆是。则益叹如公梃然为出石之笋者。不可复得也。自余来朗州。与公乡接壤。求识其子孙甚切。已而公之二孙尚铉,尚焌屡访余服舍。余喜其不替先谊也。一日二君谓余曰。弊居临水有亭。曰碧流祖父尝构竹为屋。实晚年栖息之所也。岁久且坏。今将易而新之。愿有以记之也。余观人家基业。未有不成于祖先而败于子孙者。况能修其坏而复其旧耶。今于二君见之。余又喜其能不坠先业也。然二君之所以承家者。其止于是耶。必也砥行砺义。以无忝祖武。然后方可谓善于堂构矣。一亭舍之坏。而尚不忍不修。则况于此而忽之哉。此二君之所宜加勉。而亦余区区之望也。余僇人也。无由一投足于残山剩水之间。以抚其苔枪雨甲之遗迹。则徒有怅想而已。因二君之请而一言寄意。又安可已也。至于山川之美。登眺之胜。非余所亲睹者。不暇述。第述公之气义余所尝慕用者。而仍勉二君以嗣守之道焉。亭本我 朝赵参判注别墅。传之外裔。为金氏所有。碧流即其旧号云。
滔滔皆是。则益叹如公梃然为出石之笋者。不可复得也。自余来朗州。与公乡接壤。求识其子孙甚切。已而公之二孙尚铉,尚焌屡访余服舍。余喜其不替先谊也。一日二君谓余曰。弊居临水有亭。曰碧流祖父尝构竹为屋。实晚年栖息之所也。岁久且坏。今将易而新之。愿有以记之也。余观人家基业。未有不成于祖先而败于子孙者。况能修其坏而复其旧耶。今于二君见之。余又喜其能不坠先业也。然二君之所以承家者。其止于是耶。必也砥行砺义。以无忝祖武。然后方可谓善于堂构矣。一亭舍之坏。而尚不忍不修。则况于此而忽之哉。此二君之所宜加勉。而亦余区区之望也。余僇人也。无由一投足于残山剩水之间。以抚其苔枪雨甲之遗迹。则徒有怅想而已。因二君之请而一言寄意。又安可已也。至于山川之美。登眺之胜。非余所亲睹者。不暇述。第述公之气义余所尝慕用者。而仍勉二君以嗣守之道焉。亭本我 朝赵参判注别墅。传之外裔。为金氏所有。碧流即其旧号云。水南寺记
月出山实罗季道诜师挂锡地也。始诜公相地之宜。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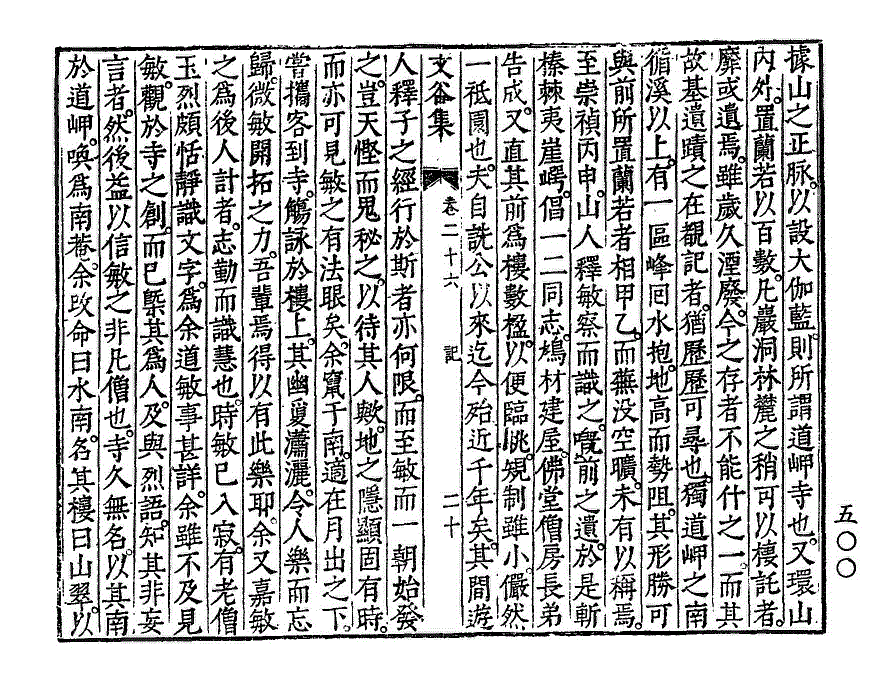 据山之正脉。以设大伽蓝。则所谓道岬寺也。又环山内外。置兰若以百数。凡岩洞林麓之稍可以栖托者。靡或遗焉。虽岁久湮废。今之存者不能什之一。而其故基遗迹之在睹记者。犹历历可寻也。独道岬之南循溪以上。有一区峰回水抱。地高而势阻。其形胜可与前所置兰若者相甲乙。而芜没空旷。未有以称焉。至崇祯丙申。山人释敏察而识之。嘅前之遗。于是斩榛棘夷崖崿。倡一二同志。鸠材建屋。佛堂僧房长弟告成。又直其前为楼数楹。以便临眺。规制虽小。俨然一祗园也。夫自诜公以来迄今殆近千年矣。其间游人释子之经行于斯者亦何限。而至敏而一朝始发之。岂天悭而鬼秘之。以待其人欤。地之隐显固有时。而亦可见敏之有法眼矣。余窜于南。适在月出之下。尝携客到寺。觞咏于楼上。其幽夐潇洒。令人乐而忘归。微敏开拓之力。吾辈焉得以有此乐耶。余又嘉敏之为后人计者。志勤而识慧也。时敏已入寂。有老僧玉烈颇恬静识文字。为余道敏事甚详。余虽不及见敏。观于寺之创而已。槩其为人。及与烈语。知其非妄言者。然后益以信敏之非凡僧也。寺久无名。以其南于道岬。唤为南庵。余改命曰水南。名其楼曰山翠。以
据山之正脉。以设大伽蓝。则所谓道岬寺也。又环山内外。置兰若以百数。凡岩洞林麓之稍可以栖托者。靡或遗焉。虽岁久湮废。今之存者不能什之一。而其故基遗迹之在睹记者。犹历历可寻也。独道岬之南循溪以上。有一区峰回水抱。地高而势阻。其形胜可与前所置兰若者相甲乙。而芜没空旷。未有以称焉。至崇祯丙申。山人释敏察而识之。嘅前之遗。于是斩榛棘夷崖崿。倡一二同志。鸠材建屋。佛堂僧房长弟告成。又直其前为楼数楹。以便临眺。规制虽小。俨然一祗园也。夫自诜公以来迄今殆近千年矣。其间游人释子之经行于斯者亦何限。而至敏而一朝始发之。岂天悭而鬼秘之。以待其人欤。地之隐显固有时。而亦可见敏之有法眼矣。余窜于南。适在月出之下。尝携客到寺。觞咏于楼上。其幽夐潇洒。令人乐而忘归。微敏开拓之力。吾辈焉得以有此乐耶。余又嘉敏之为后人计者。志勤而识慧也。时敏已入寂。有老僧玉烈颇恬静识文字。为余道敏事甚详。余虽不及见敏。观于寺之创而已。槩其为人。及与烈语。知其非妄言者。然后益以信敏之非凡僧也。寺久无名。以其南于道岬。唤为南庵。余改命曰水南。名其楼曰山翠。以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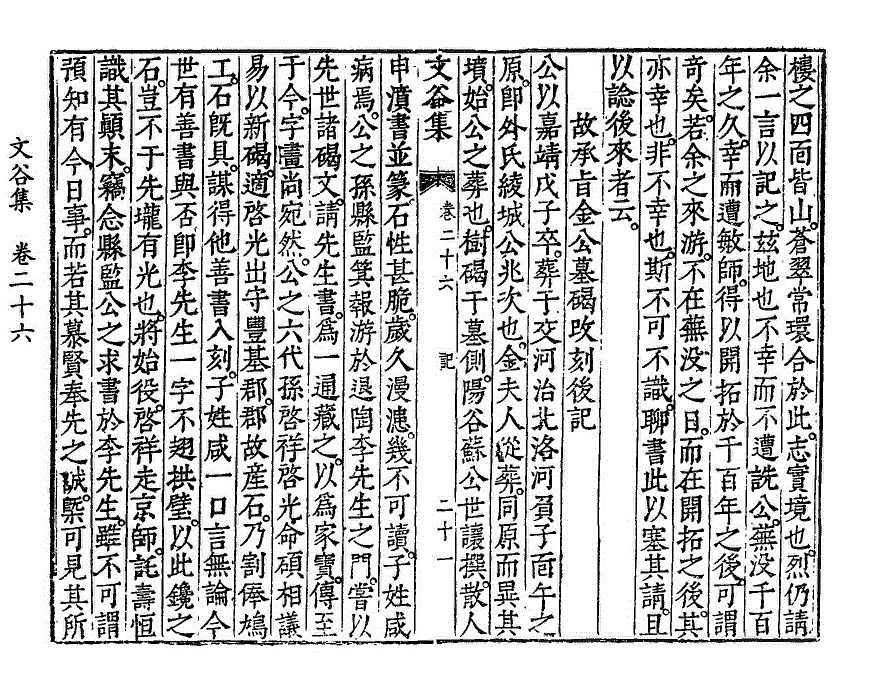 楼之四面皆山。苍翠常环合于此。志实境也。烈仍请余一言以记之。玆地也不幸而不遭诜公。芜没千百年之久。幸而遭敏师。得以开拓于千百年之后。可谓奇矣。若余之来游。不在芜没之日。而在开拓之后。其亦幸也。非不幸也。斯不可不识。聊书此以塞其请。且以谂后来者云。
楼之四面皆山。苍翠常环合于此。志实境也。烈仍请余一言以记之。玆地也不幸而不遭诜公。芜没千百年之久。幸而遭敏师。得以开拓于千百年之后。可谓奇矣。若余之来游。不在芜没之日。而在开拓之后。其亦幸也。非不幸也。斯不可不识。聊书此以塞其请。且以谂后来者云。故承旨金公墓碣改刻后记
公以嘉靖戊子卒。葬于交河治北洛河负子面午之原。即外氏绫城公兆次也。金夫人从葬。同原而异其坟。始公之葬也。树碣于墓侧。阳谷苏公世让撰。散人申濆书并篆。石性甚脆。岁久漫漶。几不可读。子姓咸病焉。公之孙县监箕报游于退陶李先生之门。尝以先世诸碣文。请先生书。为一通藏之。以为家宝。传至于今。字画尚宛然。公之六代孙启祥,启光,命硕相议易以新碣。适启光出守丰基郡。郡故产石。乃割俸鸠工。石既具。谋得他善书入刻。子姓成一口言无论今世有善书与否即李先生一字不翅拱璧。以此镵之石。岂不于先垄有光也。将始役。启祥走京师。托寿恒识其颠末。窃念县监公之求书于李先生。虽不可谓预知有今日事。而若其慕贤奉先之诚。槩可见其所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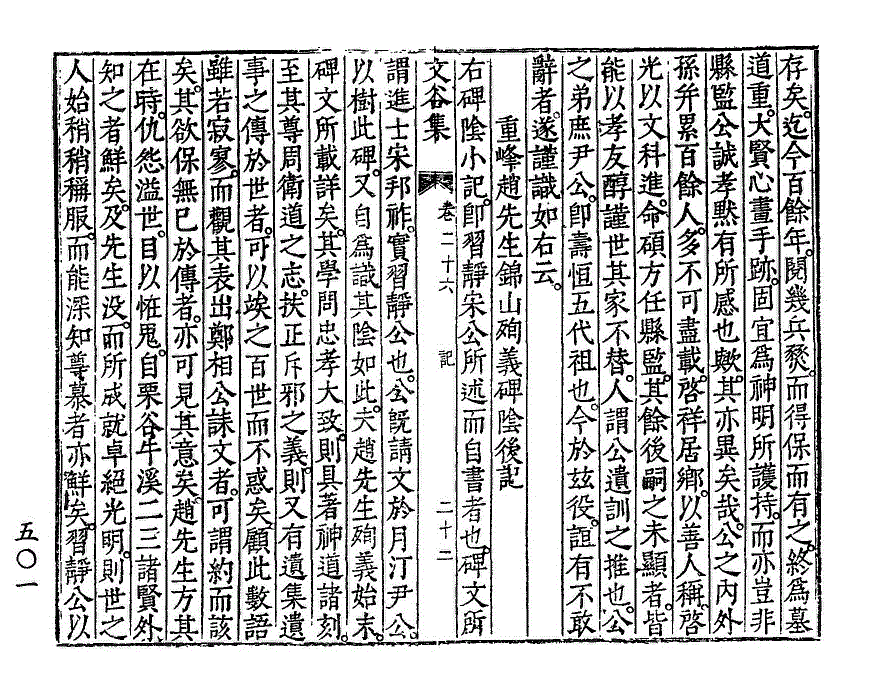 存矣。迄今百馀年。阅几兵燹。而得保而有之。终为墓道重。大贤心画手迹。固宜为神明所护持。而亦岂非县监公诚孝默有所感也欤。其亦异矣哉。公之内外孙并累百馀人。多不可尽载。启祥居乡。以善人称。启光以文科进。命硕方任县监。其馀后嗣之未显者。皆能以孝友醇谨世其家不替。人谓公遗训之推也。公之弟庶尹公。即寿恒五代祖也。今于玆役。谊有不敢辞者。遂谨识如右云。
存矣。迄今百馀年。阅几兵燹。而得保而有之。终为墓道重。大贤心画手迹。固宜为神明所护持。而亦岂非县监公诚孝默有所感也欤。其亦异矣哉。公之内外孙并累百馀人。多不可尽载。启祥居乡。以善人称。启光以文科进。命硕方任县监。其馀后嗣之未显者。皆能以孝友醇谨世其家不替。人谓公遗训之推也。公之弟庶尹公。即寿恒五代祖也。今于玆役。谊有不敢辞者。遂谨识如右云。重峰赵先生锦山殉义碑阴后记
右碑阴小记。即习静宋公所述而自书者也。碑文所谓进士宋邦祚。实习静公也。公既请文于月汀尹公。以树此碑。又自为识其阴如此。夫赵先生殉义始末。碑文所载详矣。其学问忠孝大致。则具著神道诸刻。至其尊周卫道之志。扶正斥邪之义。则又有遗集遗事之传于世者。可以俟之百世而不惑矣。顾此数语虽若寂寥。而观其表出郑相公诔文者。可谓约而该矣。其欲保无已于传者。亦可见其意矣。赵先生方其在时。仇怨溢世。目以怪鬼。自栗谷,牛溪二三诸贤外。知之者鲜矣。及先生没。而所成就卓绝光明。则世之人始稍稍称服。而能深知尊慕者亦鲜矣。习静公以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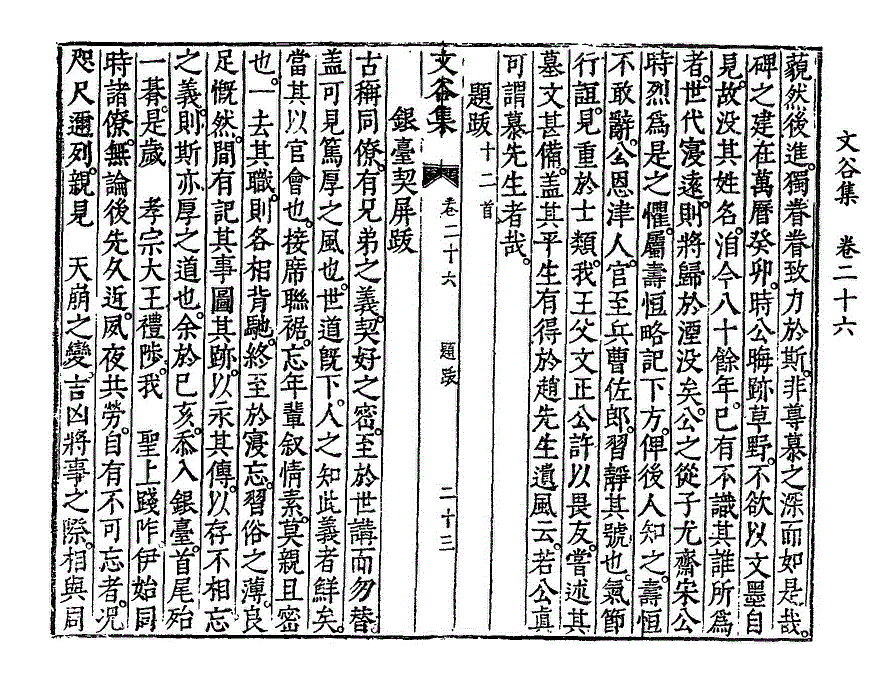 藐然后进。独眷眷致力于斯。非尊慕之深而如是哉。碑之建在万历癸卯。时公晦迹草野。不欲以文墨自见。故没其姓名。洎今八十馀年。已有不识其谁所为者。世代寖远。则将归于湮没矣。公之从子尤斋宋公时烈为是之惧。属寿恒略记下方。俾后人知之。寿恒不敢辞。公恩津人。官至兵曹佐郎。习静其号也。气节行谊。见重于士类。我王父文正公许以畏友。尝述其墓文甚备。盖其平生有得于赵先生遗风云。若公真可谓慕先生者哉。
藐然后进。独眷眷致力于斯。非尊慕之深而如是哉。碑之建在万历癸卯。时公晦迹草野。不欲以文墨自见。故没其姓名。洎今八十馀年。已有不识其谁所为者。世代寖远。则将归于湮没矣。公之从子尤斋宋公时烈为是之惧。属寿恒略记下方。俾后人知之。寿恒不敢辞。公恩津人。官至兵曹佐郎。习静其号也。气节行谊。见重于士类。我王父文正公许以畏友。尝述其墓文甚备。盖其平生有得于赵先生遗风云。若公真可谓慕先生者哉。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题跋(十二首)
银台契屏跋
古称同僚。有兄弟之义。契好之密。至于世讲而勿替。盖可见笃厚之风也。世道既下。人之知此义者鲜矣。当其以官会也。接席联裾。忘年辈叙情素。莫亲且密也。一去其职。则各相背驰。终至于寖忘。习俗之薄。良足慨然。间有记其事图其迹。以永其传。以存不相忘之义。则斯亦厚之道也。余于己亥。忝入银台。首尾殆一期。是岁 孝宗大王礼陟。我 圣上践阼。伊始同时诸僚。无论后先久近。夙夜共劳。自有不可忘者。况咫尺迩列。亲见 天崩之变。吉凶将事之际。相与周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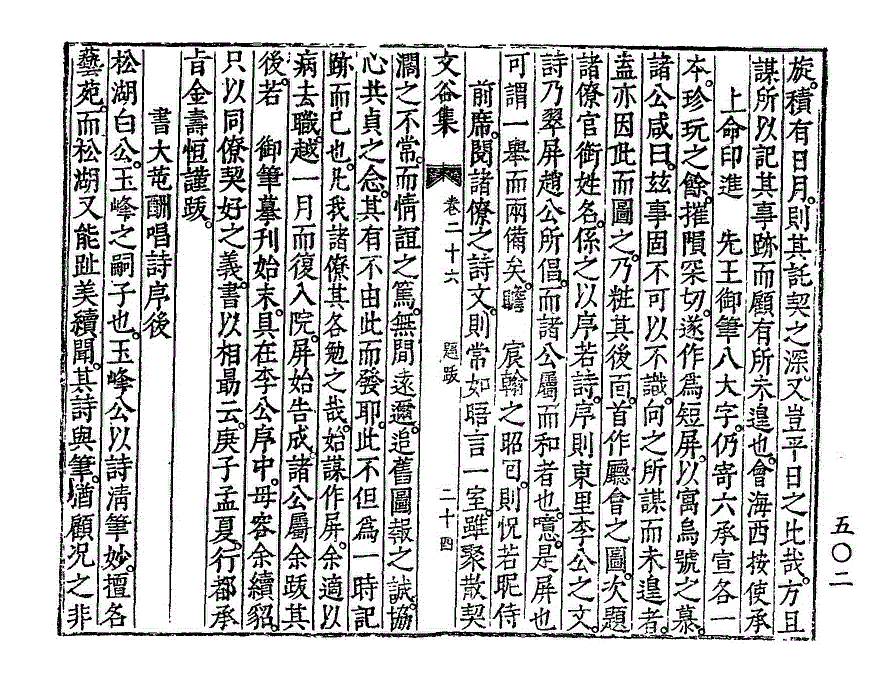 旋。积有日月。则其托契之深。又岂平日之比哉。方且谋所以记其事迹而顾有所未遑也。会海西按使承 上命印进 先王御笔八大字。仍寄六承宣各一本。珍玩之馀。摧陨深切。遂作为短屏。以寓乌号之慕。诸公咸曰。玆事固不可以不识。向之所谋而未遑者。盍亦因此而图之。乃妆其后面。首作厅会之图。次题诸僚官衔姓名。系之以序若诗。序则东里李公之文。诗乃翠屏赵公所倡。而诸公属而和者也。噫。是屏也可谓一举而两备矣。瞻 宸翰之昭回。则恍若昵侍 前席。阅诸僚之诗文。则常如晤言一室。虽聚散契阔之不常。而情谊之笃。无间远迩。追旧图报之诚。协心共贞之念。其有不由此而发耶。此不但为一时记迹而已也。凡我诸僚其各勉之哉。始谋作屏。余适以病去职。越一月而复入院。屏始告成。诸公属余跋其后。若 御笔摹刊始末。具在李公序中。毋容余续貂。只以同僚契好之义。书以相勖云。庚子孟夏。行都承旨金寿恒谨跋。
旋。积有日月。则其托契之深。又岂平日之比哉。方且谋所以记其事迹而顾有所未遑也。会海西按使承 上命印进 先王御笔八大字。仍寄六承宣各一本。珍玩之馀。摧陨深切。遂作为短屏。以寓乌号之慕。诸公咸曰。玆事固不可以不识。向之所谋而未遑者。盍亦因此而图之。乃妆其后面。首作厅会之图。次题诸僚官衔姓名。系之以序若诗。序则东里李公之文。诗乃翠屏赵公所倡。而诸公属而和者也。噫。是屏也可谓一举而两备矣。瞻 宸翰之昭回。则恍若昵侍 前席。阅诸僚之诗文。则常如晤言一室。虽聚散契阔之不常。而情谊之笃。无间远迩。追旧图报之诚。协心共贞之念。其有不由此而发耶。此不但为一时记迹而已也。凡我诸僚其各勉之哉。始谋作屏。余适以病去职。越一月而复入院。屏始告成。诸公属余跋其后。若 御笔摹刊始末。具在李公序中。毋容余续貂。只以同僚契好之义。书以相勖云。庚子孟夏。行都承旨金寿恒谨跋。书大芚酬唱诗序后
松湖白公。玉峰之嗣子也。玉峰公以诗清笔妙。擅名艺苑。而松湖又能趾美续闻。某诗与笔。犹顾况之非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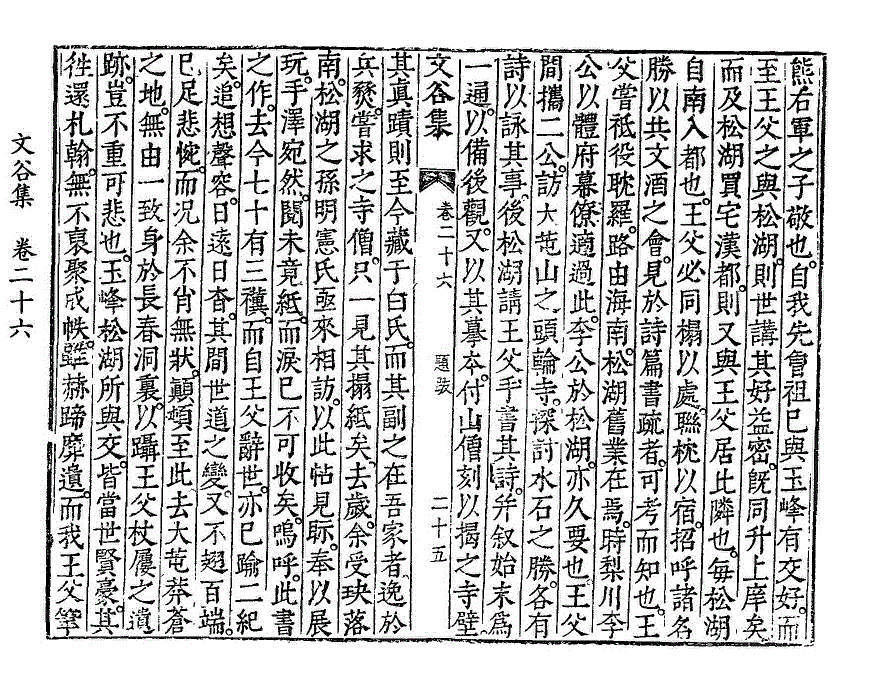 熊,右军之子敬也。自我先曾祖已与玉峰有交好。而至王父之与松湖。则世讲其好益密。既同升上庠矣而及松湖买宅汉都。则又与王父居比邻也。每松湖自南入都也。王父必同榻以处。联枕以宿。招呼诸名胜以共文酒之会。见于诗篇书疏者。可考而知也。王父尝祗役耽罗。路由海南。松湖旧业在焉。时梨川李公以体府幕僚适过此。李公于松湖。亦久要也。王父间携二公。访大芚山之头轮寺。探诗水石之胜。各有诗以咏其事。后松湖请王父手书其诗。并叙始末为一通。以备后观。又以其摹本。付山僧刻以揭之寺壁。其真迹则至今藏于白氏。而其副之在吾家者。逸于兵燹。尝求之寺僧。只一见其拓纸矣。去岁。余受玦落南。松湖之孙明宪氏亟来相访。以此帖见视。奉以展玩。手泽宛然。阅未竟纸。而泪已不可收矣。呜呼。此书之作。去今七十有三䙫。而自王父辞世。亦已踰二纪矣。追想声容。日远日杳。其间世道之变。又不翅百端。已足悲惋。而况余不肖无状。颠顿至此去大芚莽苍之地。无由一致身于长春洞里。以蹑王父杖屦之遗迹。岂不重可悲也。玉峰松湖所与交。皆当世贤豪。其往还札翰。无不裒聚成帙。虽赫蹄靡遗而我王父笔
熊,右军之子敬也。自我先曾祖已与玉峰有交好。而至王父之与松湖。则世讲其好益密。既同升上庠矣而及松湖买宅汉都。则又与王父居比邻也。每松湖自南入都也。王父必同榻以处。联枕以宿。招呼诸名胜以共文酒之会。见于诗篇书疏者。可考而知也。王父尝祗役耽罗。路由海南。松湖旧业在焉。时梨川李公以体府幕僚适过此。李公于松湖。亦久要也。王父间携二公。访大芚山之头轮寺。探诗水石之胜。各有诗以咏其事。后松湖请王父手书其诗。并叙始末为一通。以备后观。又以其摹本。付山僧刻以揭之寺壁。其真迹则至今藏于白氏。而其副之在吾家者。逸于兵燹。尝求之寺僧。只一见其拓纸矣。去岁。余受玦落南。松湖之孙明宪氏亟来相访。以此帖见视。奉以展玩。手泽宛然。阅未竟纸。而泪已不可收矣。呜呼。此书之作。去今七十有三䙫。而自王父辞世。亦已踰二纪矣。追想声容。日远日杳。其间世道之变。又不翅百端。已足悲惋。而况余不肖无状。颠顿至此去大芚莽苍之地。无由一致身于长春洞里。以蹑王父杖屦之遗迹。岂不重可悲也。玉峰松湖所与交。皆当世贤豪。其往还札翰。无不裒聚成帙。虽赫蹄靡遗而我王父笔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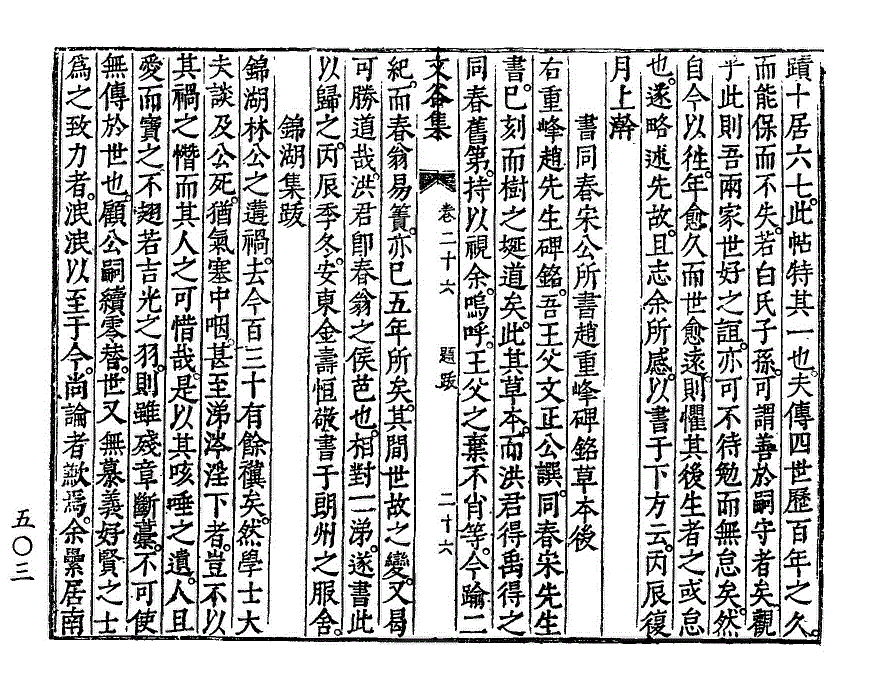 迹十居六七。此帖特其一也。夫传四世历百年之久。而能保而不失。若白氏子孙。可谓善于嗣守者矣。观乎此则吾两家世好之谊。亦可不待勉而无怠矣。然自今以往。年愈久而世愈远。则惧其后生者之或怠也。遂略述先故。且志余所感。以书于下方云。丙辰复月上浣。
迹十居六七。此帖特其一也。夫传四世历百年之久。而能保而不失。若白氏子孙。可谓善于嗣守者矣。观乎此则吾两家世好之谊。亦可不待勉而无怠矣。然自今以往。年愈久而世愈远。则惧其后生者之或怠也。遂略述先故。且志余所感。以书于下方云。丙辰复月上浣。书同春宋公所书赵重峰碑铭草本后
右重峰赵先生碑铭。吾王父文正公撰。同春宋先生书。己刻而树之埏道矣。此其草本。而洪君得禹得之同春旧第。持以视余。呜呼。王父之弃不肖等。今踚二纪。而春翁易箦。亦已五年所矣。其间世故之变。又曷可胜道哉。洪君即春翁之侯芭也。相对二涕。遂书此以归之。丙辰季冬。安东金寿恒敬书于朗州之服舍。
锦湖集跋
锦湖林公之遘祸。去今百三十有馀䙫矣。然学士大夫谈及公死。犹气塞中咽。甚至涕涔淫下者。岂不以其祸之憯而其人之可惜哉。是以其咳唾之遗。人且爱而宝之。不翅若吉光之羽。则虽残章断藁。不可使无传于世也。顾公嗣续零替。世又无慕义好贤之士为之致力者。泯泯以至于今。尚论者歉焉。余累居南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4H 页
 荒。有柳生应寿来过。即公弥甥也。袖示公诗文一册。属余正其淆讹。且掇公遗事以附卷末。余愧非其任。而亦不敢终辞也。会李公敏叙出牧光山。亟取以镂板。又为文冠其首以阐扬之。若李公真所谓慕义好贤者哉。既讫工。柳生又要余一言。余之所欲言。李公之文已尽之。奚余言之赘。抑余窃有感于心者。公之豪才直气。耸拔一世。一世之所相爱重者。无非名贤胜流。观于附录诸诗文可知焉。则于公之死。其哀之惜之固也。至以戎落之丑类。犹知怀其惠而叹其死。则不亦卓卓乎尤奇哉。况去其死百数十年之久。而犹中咽涕下。以至残章断藁。且爱玩之。必欲传于世者。其又孰使之然耶。此无他。秉彝好德之同其心。而无殊俗旷世之间也若是。则彼接武同朝。袭冠裳诵诗书。而乃反仇视蜮何。必揃刈之为快者。独何心哉。噫。欧阳氏之言曰。士之生死。岂其一身之事哉。若公生死。诚可谓关于世道。而其生而爱之。死而惜之者。又非特为公一身地也。至于仇贤逞祸之辈。其好恶之天。亦岂独殊于人哉。唯急于快一己之私而不暇他顾也。一念毫忽之差。而其流之祸遂至于此。后之览斯集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且余因此而重有嘅焉。
荒。有柳生应寿来过。即公弥甥也。袖示公诗文一册。属余正其淆讹。且掇公遗事以附卷末。余愧非其任。而亦不敢终辞也。会李公敏叙出牧光山。亟取以镂板。又为文冠其首以阐扬之。若李公真所谓慕义好贤者哉。既讫工。柳生又要余一言。余之所欲言。李公之文已尽之。奚余言之赘。抑余窃有感于心者。公之豪才直气。耸拔一世。一世之所相爱重者。无非名贤胜流。观于附录诸诗文可知焉。则于公之死。其哀之惜之固也。至以戎落之丑类。犹知怀其惠而叹其死。则不亦卓卓乎尤奇哉。况去其死百数十年之久。而犹中咽涕下。以至残章断藁。且爱玩之。必欲传于世者。其又孰使之然耶。此无他。秉彝好德之同其心。而无殊俗旷世之间也若是。则彼接武同朝。袭冠裳诵诗书。而乃反仇视蜮何。必揃刈之为快者。独何心哉。噫。欧阳氏之言曰。士之生死。岂其一身之事哉。若公生死。诚可谓关于世道。而其生而爱之。死而惜之者。又非特为公一身地也。至于仇贤逞祸之辈。其好恶之天。亦岂独殊于人哉。唯急于快一己之私而不暇他顾也。一念毫忽之差。而其流之祸遂至于此。后之览斯集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且余因此而重有嘅焉。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4L 页
 公之墓在锦水之上。而尚未有数尺之碣。揭诸阡隧。此行路之所嗟惋也。倘复有慕义好贤如李公者出。而图所以记载。使百世之后。知公化碧之藏在是。则岂不益可以树风声昭来许哉。李公既倡之于前。继其后者。岂无其人欤。余将有待焉。
公之墓在锦水之上。而尚未有数尺之碣。揭诸阡隧。此行路之所嗟惋也。倘复有慕义好贤如李公者出。而图所以记载。使百世之后。知公化碧之藏在是。则岂不益可以树风声昭来许哉。李公既倡之于前。继其后者。岂无其人欤。余将有待焉。题李生松齐篆章帖
篆刻固小技也。然孔子日。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此甚责其无所用心者也。况于今得睹仓籀遗法。尚赖有此。则又曷可少哉。余素不娴篆书。而其好之几乎癖。尝窃怪世之人于博奕多好之。而视此反有不屑也。今来朗州。有李生松齐数相从。因知其善于斯艺。一日袖示此帖。皆其手刻。个个精妙。今世所罕见也。余既爱玩之不足。且喜其同好。书此以归之。然李生不徒以贤乎。己为能。而又能知所用心而有进焉则几矣。李生勉乎哉。
书罗别坐海凤与溪谷酬唱诗帖后
余尝见溪谷集中。与罗同年应瑞酬唱诸作最多。而不知罗公为何如人也。乙卯。余南迁过锦城。有罗生相器,世器手一帖来示。即其王父南涧公与溪谷往复诗札也。南涧即罗公自号。而溪谷少与同升庠。及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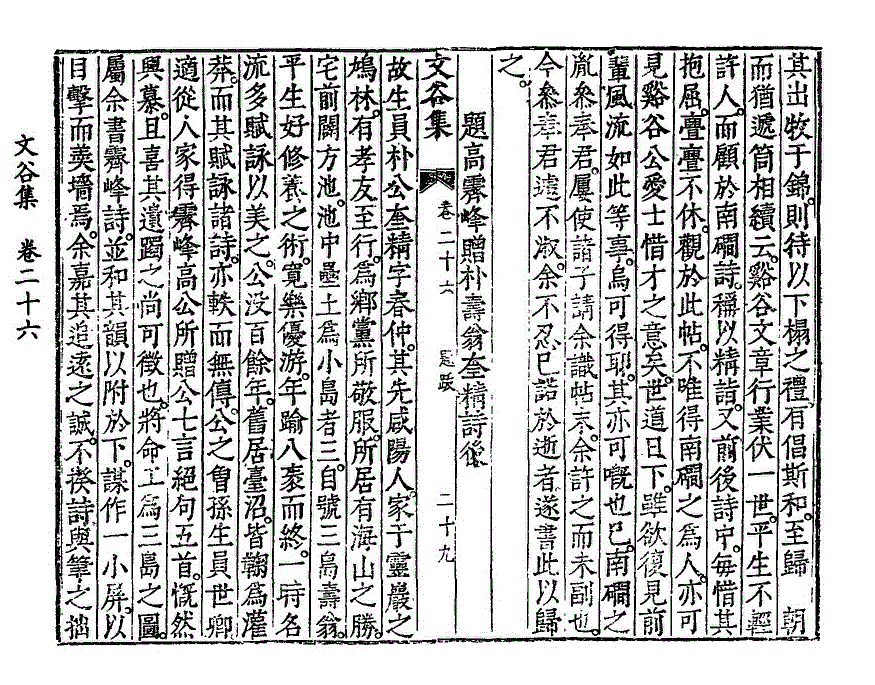 其出牧于锦。则待以下榻之礼有倡斯和。至归 朝而犹递筒相续云。溪谷文章行业伏一世。平生不轻许人。而顾于南涧诗。称以精诣。又前后诗中。每惜其抱屈。亹亹不休。观于此帖。不唯得南涧之为人。亦可见溪谷公爱士惜才之意矣。世道日下。虽欲复见前辈风流如此等事。乌可得耶。其亦可嘅也已。南涧之胤参奉君。屡使诸子请余识帖末。余许之而未副也。今参奉君遽不淑。余不忍已诺于逝者。遂书此以归之。
其出牧于锦。则待以下榻之礼有倡斯和。至归 朝而犹递筒相续云。溪谷文章行业伏一世。平生不轻许人。而顾于南涧诗。称以精诣。又前后诗中。每惜其抱屈。亹亹不休。观于此帖。不唯得南涧之为人。亦可见溪谷公爱士惜才之意矣。世道日下。虽欲复见前辈风流如此等事。乌可得耶。其亦可嘅也已。南涧之胤参奉君。屡使诸子请余识帖末。余许之而未副也。今参奉君遽不淑。余不忍已诺于逝者。遂书此以归之。题高霁峰赠朴寿翁奎精诗后
故生员朴公奎精字春仲。其先咸阳人。家于灵岩之鸠林。有孝友至行。为乡党所敬服。所居有海山之胜。宅前辟方池。池中垒土为小岛者三。自号三岛寿翁。平生好修养之术。宽乐优游。年踰八帙而终。一时名流多赋咏以美之。公没百馀年。旧居台沼。皆鞠为灌莽。而其赋咏诸诗。亦轶而无传。公之曾孙生员世卿。适从人家得霁峰高公所赠公七言绝句五首。慨然兴慕。且喜其遗躅之尚可徵也。将命工为三岛之图。属余书霁峰诗。并和其韵以附于下。谋作一小屏。以目击而羹墙焉。余嘉其追远之诚。不揆诗与笔之拙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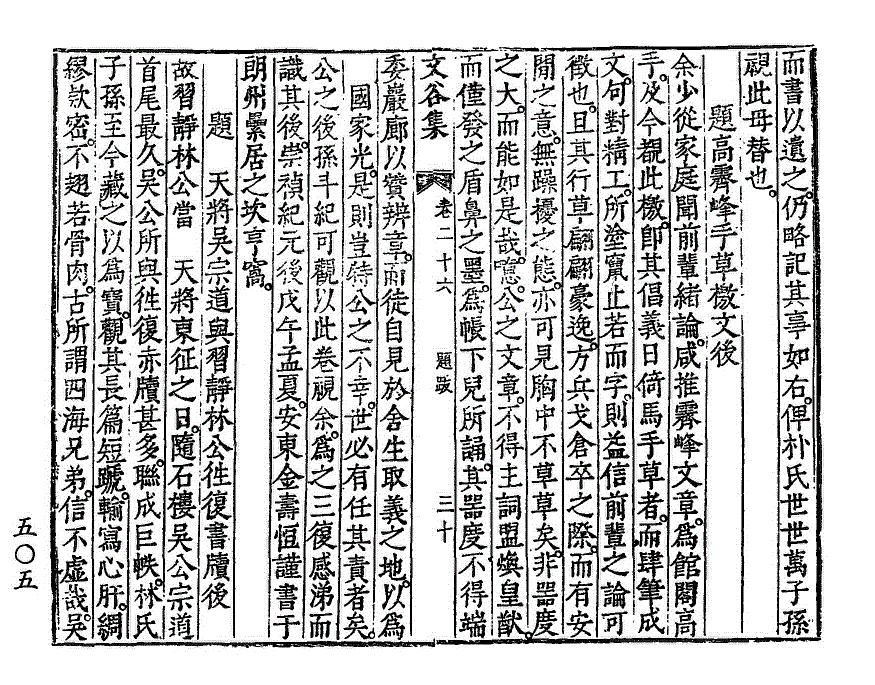 而书以遗之。仍略记其事如右。俾朴氏世世万子孙视此毋替也。
而书以遗之。仍略记其事如右。俾朴氏世世万子孙视此毋替也。题高霁峰手草檄文后
余少从家庭闻前辈绪论。咸推霁峰文章。为馆阁高手。及今睹此檄。即其倡义日。倚马手草者。而肆笔成文。句对精工。所涂窜止若而字。则益信前辈之论可徵也。且其行草翩翩豪逸。方兵戈仓卒之际。而有安閒之意。无躁扰之态。亦可见胸中不草草矣。非器度之大。而能如是哉。噫。公之文章。不得主词盟焕皇猷。而仅发之盾鼻之墨。为帐下儿所诵。其器度不得端委岩廊以赞辨章。而徒自见于舍生取义之地。以为 国家光。是则岂特公之不幸。世必有任其责者矣。公之后孙斗纪可观以此卷视余。为之三复感涕而识其后。崇祯纪元后戊午孟夏。安东金寿恒谨书于朗州累居之坎亨窝。
题 天将吴宗道与习静林公往复书牍后
故习静林公当 天将东征之日。随石楼吴公宗道首尾最久。吴公所与往复赤牍甚多。联成巨帙。林氏子孙至今藏之以为宝。观其长篇短蹄。输写心肝。绸缪款密。不翅若骨肉。古所谓四海兄弟。信不虚哉。吴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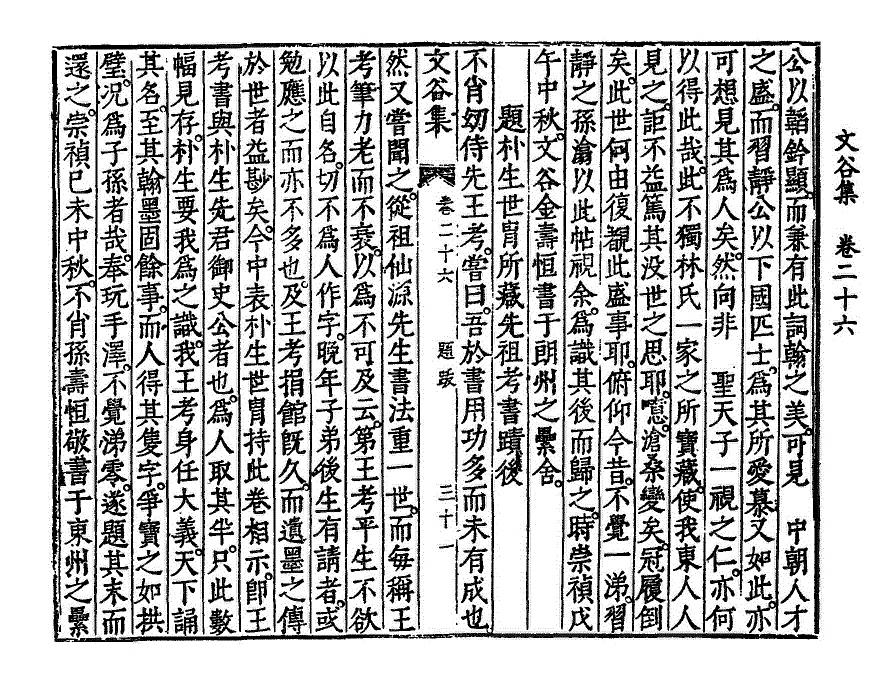 公以韬钤显。而兼有此词翰之美。可见 中朝人才之盛。而习静公以下国匹士。为其所爱慕又如此。亦可想见其为人矣。然向非 圣天子一视之仁。亦何以得此哉。此不独林氏一家之所宝藏。使我东人人见之。讵不益笃其没世之思耶。噫。沧桑变矣。冠履倒矣。此世何由复睹此盛事耶。俯仰今昔。不觉一涕。习静之孙潝以此帖视余。为识其后而归之。时崇祯戊午中秋。文谷金寿恒书于朗州之累舍。
公以韬钤显。而兼有此词翰之美。可见 中朝人才之盛。而习静公以下国匹士。为其所爱慕又如此。亦可想见其为人矣。然向非 圣天子一视之仁。亦何以得此哉。此不独林氏一家之所宝藏。使我东人人见之。讵不益笃其没世之思耶。噫。沧桑变矣。冠履倒矣。此世何由复睹此盛事耶。俯仰今昔。不觉一涕。习静之孙潝以此帖视余。为识其后而归之。时崇祯戊午中秋。文谷金寿恒书于朗州之累舍。题朴生世胄所藏先祖考书迹后
不肖幼侍先王考。尝曰。吾于书用功多而未有成也。然又尝闻之。从祖仙源先生书法重一世。而每称王考笔力老而不衰。以为不可及云。第王考平生不欲以此自名。切不为人作字。晚年子弟后生有请者。或勉应之而亦不多也。及王考捐馆既久。而遗墨之传于世者益鲜矣。今中表朴生世冑持此卷相示。即王考书与朴生先君御史公者也。为人取其半。只此数幅见存。朴生要我为之识。我王考身任大义。天下诵其名。至其翰墨固馀事。而人得其只字。争宝之如拱璧。况为子孙者哉。奉玩手泽。不觉涕零。遂题其末而还之。崇祯己未中秋。不肖孙寿恒敬书于东州之累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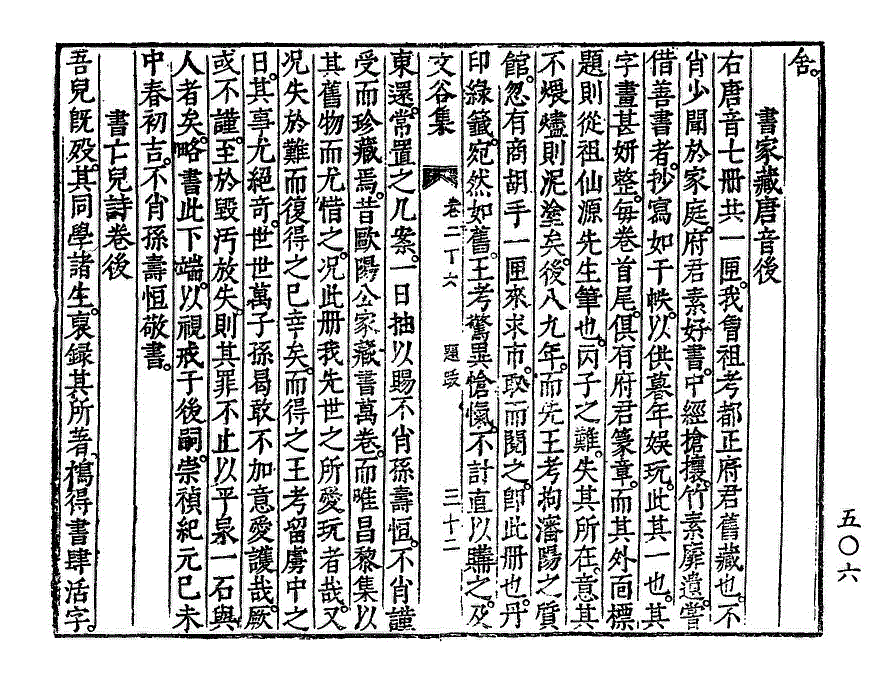 舍。
舍。书家藏唐音后
右唐音七册共一匣。我曾祖考都正府君旧藏也。不肖少闻于家庭。府君素好书。中经抢攘。竹素靡遗。尝借善书者。抄写如干帙。以供暮年娱玩。此其一也。其字画甚妍整。每卷首尾。俱有府君篆章。而其外面标题则从祖仙源先生笔也。丙子之难。失其所在。意其不煨烬则泥涂矣。后八九年。而先王考拘沈阳之质馆。忽有商胡手一匣来求市。取而阅之。即此册也。丹印绿签。宛然如旧。王考惊异怆忾。不计直以购之。及东还。常置之几案。一日抽以赐不肖孙寿恒。不肖谨受而珍藏焉。昔欧阳公家藏书万卷。而唯昌黎集以其旧物而尤惜之。况此册我先世之所爱玩者哉。又况失于难而复得之已幸矣。而得之王考留虏中之日。其事尤绝奇。世世万子孙曷敢不加意爱护哉。厥或不谨。至于毁污放失。则其罪不止以平泉一石与人者矣。略书此下端。以视戒于后嗣。崇祯纪元己未中春初吉。不肖孙寿恒敬书。
书亡儿诗卷后
吾儿既殁。其同学诸生。裒录其所著。鸠得书肆活字。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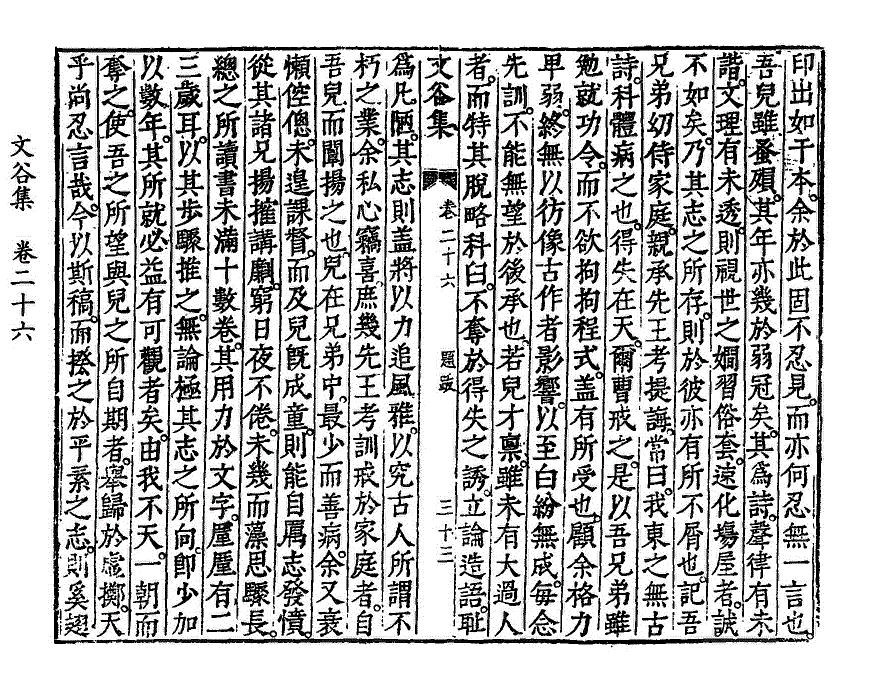 印出如干本。余于此固不忍见。而亦何忍无一言也。吾儿虽蚤殒。其年亦几于弱冠矣。其为诗。声律有未谐。文理有未透。则视世之娴习俗套。速化场屋者。诚不如矣。乃其志之所存。则于彼亦有所不屑也。记吾兄弟幼侍家庭。亲承先王考提诲。常曰。我东之无古诗。科体病之也。得失在天。尔曹戒之。是以吾兄弟虽勉就功令。而不欲拘拘程式。盖有所受也。顾余格力卑弱。终无以彷像古作者影响。以至白纷无成。每念先训。不能无望于后承也。若儿才禀。虽未有大过人者。而特其脱略科臼。不夺于得失之诱。立论造语。耻为凡陋。其志则盖将以力追风雅。以究古人所谓不朽之业。余私心窃喜。庶几先王考训戒于家庭者。自吾儿而阐扬之也。儿在兄弟中。最少而善病。余又衰懒倥偬。未遑课督。而及儿既成童。则能自厉志发愤。从其诸兄扬搉讲劘。穷日夜不倦。未几而藻思骤长。总之所读书未满十数卷。其用力于文字。廑廑有二三岁耳。以其步骤推之。无论极其志之所向。即少加以数年。其所就必益有可观者矣。由我不天。一朝而夺之。使吾之所望与儿之所自期者。举归于虚掷。天乎尚忍言哉。今以斯稿。而揆之于平素之志。则奚翅
印出如干本。余于此固不忍见。而亦何忍无一言也。吾儿虽蚤殒。其年亦几于弱冠矣。其为诗。声律有未谐。文理有未透。则视世之娴习俗套。速化场屋者。诚不如矣。乃其志之所存。则于彼亦有所不屑也。记吾兄弟幼侍家庭。亲承先王考提诲。常曰。我东之无古诗。科体病之也。得失在天。尔曹戒之。是以吾兄弟虽勉就功令。而不欲拘拘程式。盖有所受也。顾余格力卑弱。终无以彷像古作者影响。以至白纷无成。每念先训。不能无望于后承也。若儿才禀。虽未有大过人者。而特其脱略科臼。不夺于得失之诱。立论造语。耻为凡陋。其志则盖将以力追风雅。以究古人所谓不朽之业。余私心窃喜。庶几先王考训戒于家庭者。自吾儿而阐扬之也。儿在兄弟中。最少而善病。余又衰懒倥偬。未遑课督。而及儿既成童。则能自厉志发愤。从其诸兄扬搉讲劘。穷日夜不倦。未几而藻思骤长。总之所读书未满十数卷。其用力于文字。廑廑有二三岁耳。以其步骤推之。无论极其志之所向。即少加以数年。其所就必益有可观者矣。由我不天。一朝而夺之。使吾之所望与儿之所自期者。举归于虚掷。天乎尚忍言哉。今以斯稿。而揆之于平素之志。则奚翅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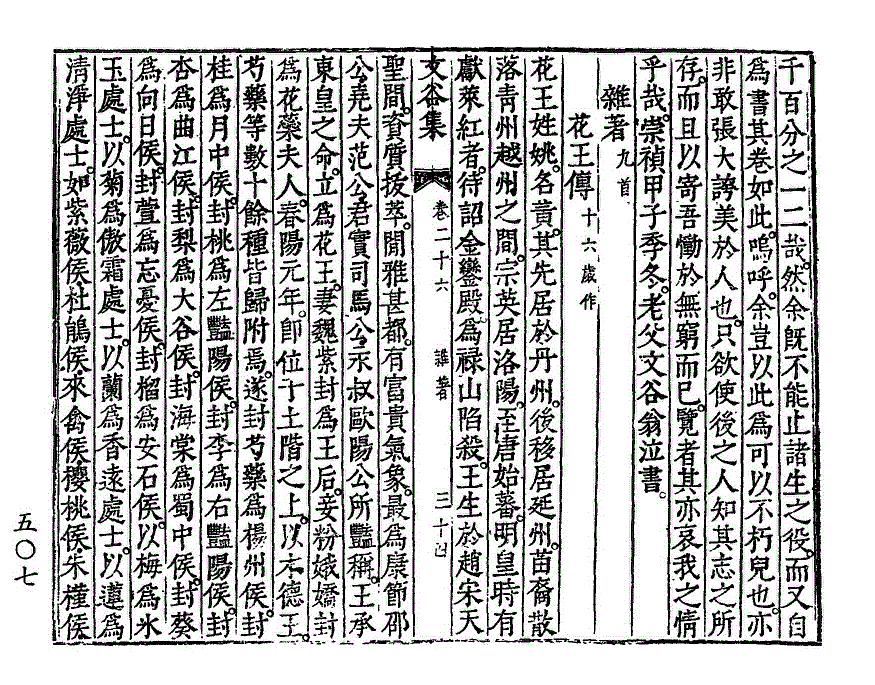 千百分之一二哉。然余既不能止诸生之役。而又自为书其卷如此。呜呼。余岂以此为可以不朽儿也。亦非敢张大誇美于人也。只欲使后之人知其志之所存。而且以寄吾恸于无穷而已。览者其亦哀我之情乎哉。崇祯甲子季冬。老父文谷翁泣书。
千百分之一二哉。然余既不能止诸生之役。而又自为书其卷如此。呜呼。余岂以此为可以不朽儿也。亦非敢张大誇美于人也。只欲使后之人知其志之所存。而且以寄吾恸于无穷而已。览者其亦哀我之情乎哉。崇祯甲子季冬。老父文谷翁泣书。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杂著(九首)
花王传(十六岁作)
花王姓姚。名黄。其先居于丹州。后移居延州。苗裔散落青州越州之间。宗英居洛阳。至唐始蕃。明皇时有献莱红者。待诏金銮殿。为禄山陷杀。王生于赵宋天圣间。资质拔萃。閒雅甚都。有富贵气象。最为康节邵公,尧夫范公,君实司马公,永叔欧阳公所艳称。王承东皇之命。立为花王。妻魏紫封为王后。妾粉娥娇封为花蕊夫人。春阳元年。即位于土阶之上。以木德王。芍药等数十馀种皆归附焉。遂封芍药为杨州侯。封桂为月中侯。封桃为左艳阳侯。封李为右艳阳侯。封杏为曲江侯。封梨为大谷侯。封海棠为蜀中侯。封葵为向日侯。封萱为忘忧侯。封榴为安石侯。以梅为冰玉处士。以菊为傲霜处士。以兰为香远处士。以莲为清净处士。如紫薇侯,杜鹃侯,来离侯,樱桃侯,朱槿侯,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8H 页
 水仙侯,牵牛侯,金凤侯,鸡冠侯,瑞香侯,含笑侯,山茶侯,栀子侯,酴醾侯,茉莉侯等。亦皆率其职焉。二年。两衙侯黄蜂,漆园侯白蝶入朝。蜂善歌蝶善舞。是日王受朝开宴。蜂奏霓裳羽衣之曲。蝶和而舞。丘隅侯黄栗留。亦以善歌笙与焉。君臣相悦。终日尽欢而罢。人皆荣之。一日。王曰左艳阳侯,右艳阳侯等谄谀妖冶。病于夏畦。其黜之。冰玉处士,傲霜处士,香远处士,清净处士。隐迹山林江湖之间。而贞操凛然。香名振于京师。其裂土而封。以褒其立懦之风。于是封梅为罗浮侯。封菊为东篱侯。封兰为九畹侯。封莲为若邪侯。皆不起而终。三年。祝融使封姨作乱于王宫。王遂殂落于土阶之下。群臣从死者甚众焉。后一年。两衙侯,漆园侯,丘隅侯入朝。则花王已亡。有殷墟黍离之叹。遂为之歌曰。昔余来朝兮。歌舞纷纷。今余来朝兮。旧迹成陈。吁嗟花王兮今已亡。一声哀歌兮空自伤。歌竟。痛哭而去。人莫不怜之。王之孙枝。流散于中国。或寄身于人家。或托迹于荆棘。更无蕃息者云。
水仙侯,牵牛侯,金凤侯,鸡冠侯,瑞香侯,含笑侯,山茶侯,栀子侯,酴醾侯,茉莉侯等。亦皆率其职焉。二年。两衙侯黄蜂,漆园侯白蝶入朝。蜂善歌蝶善舞。是日王受朝开宴。蜂奏霓裳羽衣之曲。蝶和而舞。丘隅侯黄栗留。亦以善歌笙与焉。君臣相悦。终日尽欢而罢。人皆荣之。一日。王曰左艳阳侯,右艳阳侯等谄谀妖冶。病于夏畦。其黜之。冰玉处士,傲霜处士,香远处士,清净处士。隐迹山林江湖之间。而贞操凛然。香名振于京师。其裂土而封。以褒其立懦之风。于是封梅为罗浮侯。封菊为东篱侯。封兰为九畹侯。封莲为若邪侯。皆不起而终。三年。祝融使封姨作乱于王宫。王遂殂落于土阶之下。群臣从死者甚众焉。后一年。两衙侯,漆园侯,丘隅侯入朝。则花王已亡。有殷墟黍离之叹。遂为之歌曰。昔余来朝兮。歌舞纷纷。今余来朝兮。旧迹成陈。吁嗟花王兮今已亡。一声哀歌兮空自伤。歌竟。痛哭而去。人莫不怜之。王之孙枝。流散于中国。或寄身于人家。或托迹于荆棘。更无蕃息者云。太史公曰。花王气度天然。威仪棣棣。待处士黜奸人。莫不得其宜。宜其长久。而数年而亡。悲夫。黄蜂之歌。同于箕子麦秀之曲。亦可尚也。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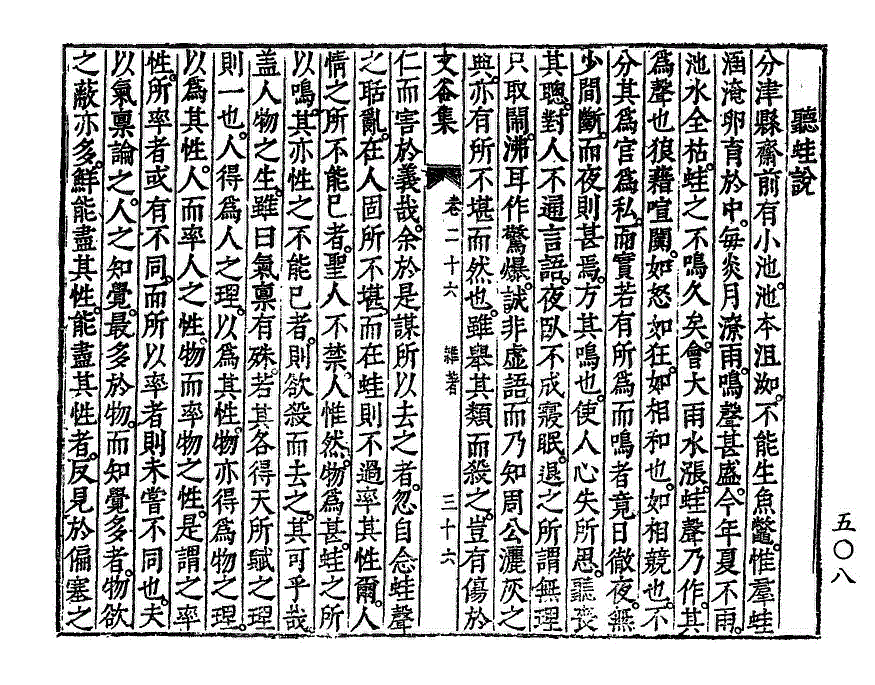 听蛙说
听蛙说分津县斋前有小池。池本沮洳。不能生鱼鳖。惟群蛙涵淹卵育于中。每炎月潦雨。鸣声甚盛。今年夏不雨。池水全枯。蛙之不鸣久矣。会大雨水涨。蛙声乃作。其为声也狼藉喧阗。如怒如狂。如相和也。如相竞也。不分其为官为私。而实若有所为而鸣者竟日彻夜。无少间断。而夜则甚焉。方其鸣也。使人心失所思。听丧其聪。对人不通言语。夜卧不成寝眠。退之所谓无理只取闹。沸耳作惊爆。诚非虚语。而乃知周公洒灰之典。亦有所不堪而然也。虽举其类而杀之。岂有伤于仁而害于义哉。余于是谋所以去之者。忽自念蛙声之聒乱。在人固所不堪。而在蛙则不过率其性尔。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圣人不禁。人惟然。物为甚。蛙之所以鸣。其亦性之不能已者。则欲杀而去之。其可乎哉。盖人物之生。虽曰气禀有殊。若其各得天所赋之理则一也。人得为人之理。以为其性。物亦得为物之理。以为其性。人而率人之性。物而率物之性。是谓之率性。所率者或有不同。而所以率者则未尝不同也。夫以气禀论之。人之知觉。最多于物。而知觉多者。物欲之蔽亦多。鲜能尽其性。能尽其性者。反见于偏塞之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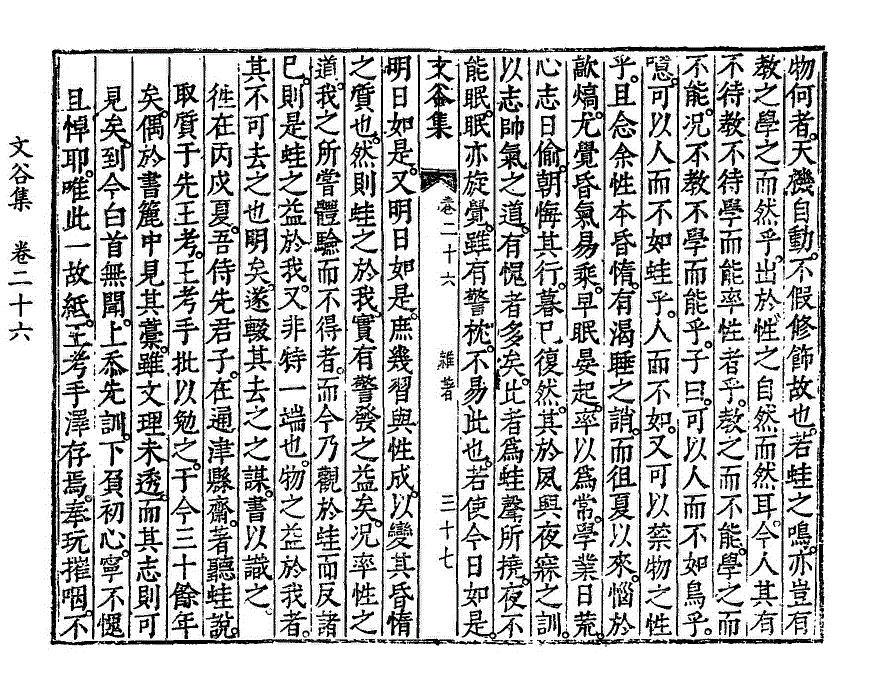 物何者。天机自动。不假修饰故也。若蛙之鸣。亦岂有教之学之而然乎。出于性之自然而然耳。今人其有不待教不待学而能率性者乎。教之而不能。学之而不能。况不教不学而能乎。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噫。可以人而不如蛙乎。人而不如。又可以禁物之性乎。且念余性本昏惰。有渴睡之诮。而徂夏以来。恼于歊熇。尤觉昏气易乘。早眠晏起。率以为常。学业日荒。心志日偷。朝悔其行。暮已复然。其于夙兴夜寐之训。以志帅气之道。有愧者多矣。比者为蛙声所挠。夜不能眠。眠亦旋觉。虽有警枕。不易此也。若使今日如是。明日如是。又明日如是。庶几习与性成。以变其昏情之质也。然则蛙之于我。实有警发之益矣。况率性之道。我之所尝体验而不得者。而今乃观于蛙而反诸己。则是蛙之益于我。又非特一端也。物之益于我者。其不可去之也明矣。遂辍其去之之谋。书以识之。
物何者。天机自动。不假修饰故也。若蛙之鸣。亦岂有教之学之而然乎。出于性之自然而然耳。今人其有不待教不待学而能率性者乎。教之而不能。学之而不能。况不教不学而能乎。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噫。可以人而不如蛙乎。人而不如。又可以禁物之性乎。且念余性本昏惰。有渴睡之诮。而徂夏以来。恼于歊熇。尤觉昏气易乘。早眠晏起。率以为常。学业日荒。心志日偷。朝悔其行。暮已复然。其于夙兴夜寐之训。以志帅气之道。有愧者多矣。比者为蛙声所挠。夜不能眠。眠亦旋觉。虽有警枕。不易此也。若使今日如是。明日如是。又明日如是。庶几习与性成。以变其昏情之质也。然则蛙之于我。实有警发之益矣。况率性之道。我之所尝体验而不得者。而今乃观于蛙而反诸己。则是蛙之益于我。又非特一端也。物之益于我者。其不可去之也明矣。遂辍其去之之谋。书以识之。往在丙戌夏。吾侍先君子。在通津县斋。著听蛙说。取质于先王考。王考手批以勉之。于今三十馀年矣。偶于书簏中见其藁。虽文理未透。而其志则可见矣。到今白首无闻。上忝先训。下负初心。宁不愧且悼耶。唯此一故纸。王考手泽存焉。奉玩摧咽。不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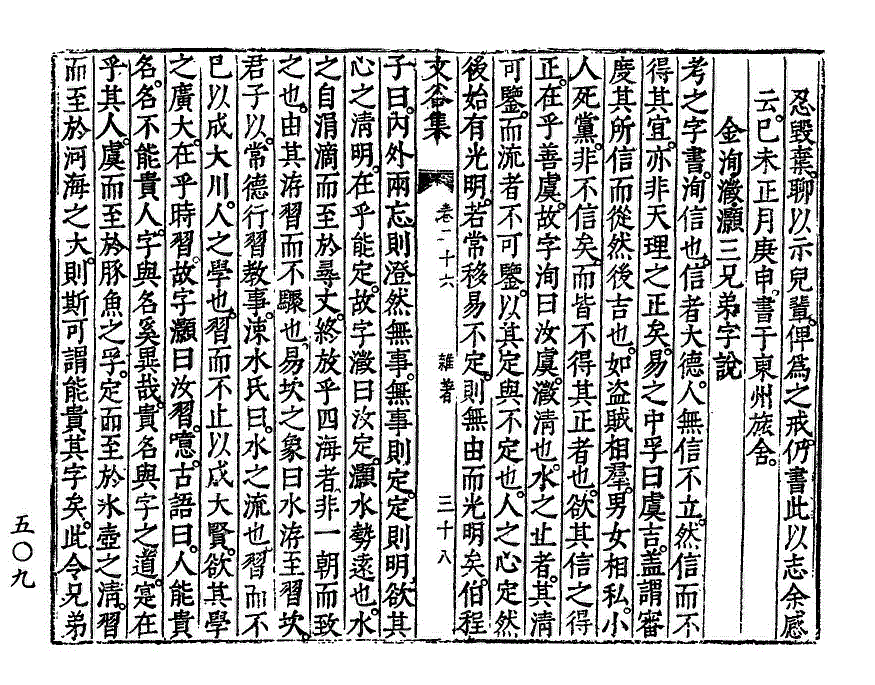 忍毁弃。聊以示儿辈。俾为之戒。仍书此以志余感云。己未正月庚申。书于东州旅舍。
忍毁弃。聊以示儿辈。俾为之戒。仍书此以志余感云。己未正月庚申。书于东州旅舍。金洵,澄,灏三兄弟字说
考之字书。洵信也。信者大德。人无信不立。然信而不得其宜。亦非天理之正矣。易之中孚曰虞吉。盖谓审度其所信而从然后吉也。如盗贼相群。男女相私。小人死党。非不信矣。而皆不得其正者也。欲其信之得正。在乎善虞。故字洵曰汝虞。澄清也。水之止者。其清可鉴。而流者不可鉴。以其定与不定也。人之心定然后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则无由而光明矣。伯程子曰。内外两忘则澄然无事。无事则定。定则明。欲其心之清明。在乎能定。故字澄曰汝定。灏水势远也。水之自涓滴而至于寻丈。终放乎四海者。非一朝而致之也。由其游习而不骤也。易坎之象曰水游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涑水氏曰。水之流也。习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欲其学之广大。在乎时习。故字灏曰汝习。噫。古语曰。人能贵名。名不能贵人。字与名奚异哉。贵名与字之道。寔在乎其人。虞而至于豚鱼之孚。定而至于冰壶之清。习而至于河海之大。则斯可谓能贵其字矣。此令兄弟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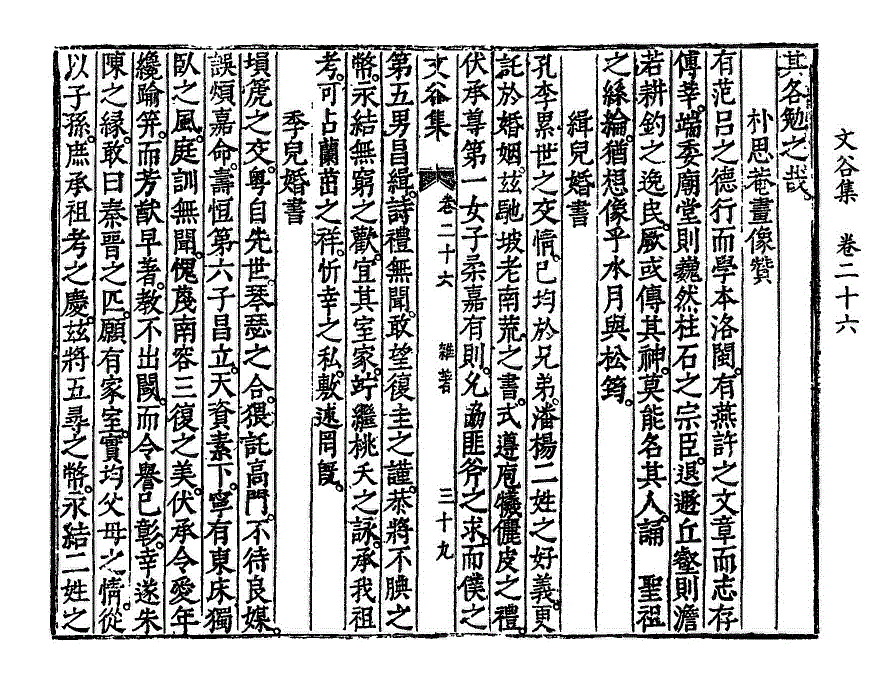 其各勉之哉。
其各勉之哉。朴思庵画像赞
有范吕之德行而学本洛闽。有燕许之文章而志存傅莘。端委庙堂则巍然柱石之宗臣。退遁丘壑则澹若耕钓之逸民。厥或传其神。莫能名其人。诵 圣祖之丝纶。犹想像乎水月与松筠。
缉儿婚书
孔李累世之交情。已均于兄弟。潘杨二姓之好义。更托于婚姻。玆驰坡老南荒之书。式遵庖牺俪皮之礼。伏承尊第一女子柔嘉有则。允协匪斧之求。而仆之第五男昌缉。诗礼无闻。敢望复圭之谨。恭将不腆之币。永结无穷之欢。宜其室家。伫继桃夭之咏。承我祖考。可占兰茁之祥。忻幸之私。敷述罔既。
季儿婚书
埙篪之交。粤自先世。琴瑟之合。猥托高门。不待良媒。误烦嘉命。寿恒第六子昌立。天资素下。宁有东床独卧之风。庭训无闻。愧蔑南容三复之美。伏承令爱年才踰笄。而芳猷早著。教不出阈。而令誉已彰。莘遂朱陈之缘。敢曰秦晋之匹。愿有家室。实均父母之情。从以子孙。庶承祖考之庆。玆将五寻之币。永结二姓之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0L 页
 欢。伏惟尊慈。俯赐鉴念。
欢。伏惟尊慈。俯赐鉴念。策问
王若曰。为国之道。必先立体统。然后朝廷尊而治道得矣。皋陶之戒丛脞于元首。文王之罔敢知于庶狱。此亦出于存体统之意欤。汉文帝之亲问钱谷。唐太宗之身兼将相。皆未免失体统。而能享治平者何欤。光武明慎政体而总揽权纲。玄宗不应姚崇而仰视殿屋。其为识体统则同。而治乱之相悬何欤。自五代迄宋。能立体统而致治者。亦可历指而详言之欤。予以否德。叨承丕基。夙夜孜孜。励精图治。制度文为。率由旧章。设官分职。各有统领。欲使无相侵踰以尊国体。而奈何体统之不严。日以益甚。百隶怠官。而玩愒成习。纲纪解弛。而庶事颓堕。等威不明。上下渐至陵替。命令不行。中外徒事姑息。国势委靡。莫可收拾。此由世道日下。人各异心而然耶。抑予为治之道。未得其要而然耶。何以则体统立而朝廷尊。以臻隆古之治欤。子大夫必有明于治体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将亲览而采择焉。
协儿赴北幕临别书赠
昔我王考当 宣庙朝。以吏部郎奉使耽罗。甫反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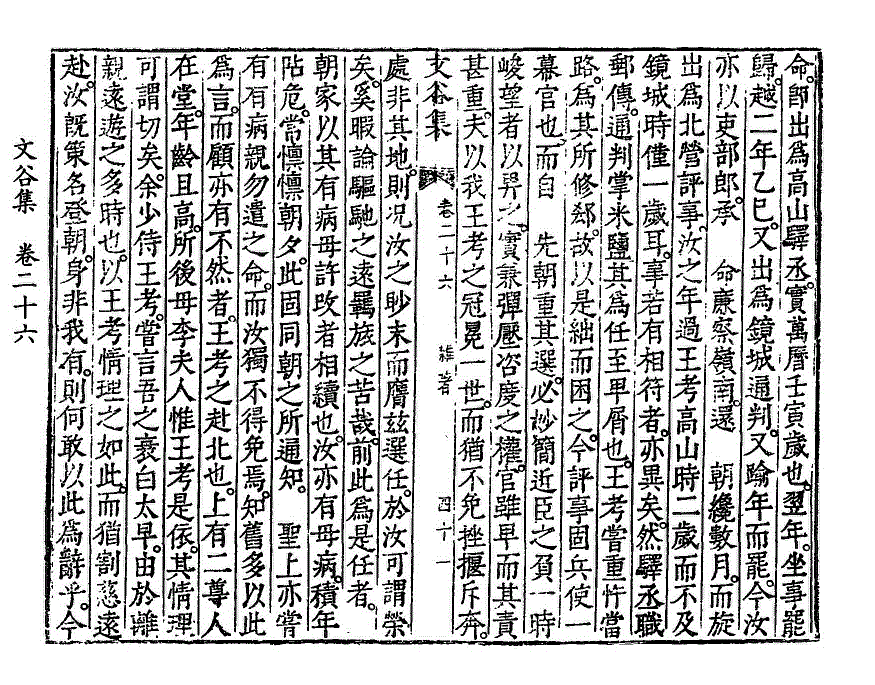 命。即出为高山驿丞。实万历壬寅岁也。翌年。坐事罢归。越二年乙巳。又出为镜城通判。又䠯年而罢。今汝亦以吏部郎。承 命廉察岭南。还 朝才数月。而旋出为北营评事。汝之年过王考高山时二岁而不及镜城时仅一岁耳。事若有相符者。亦异矣。然驿丞职邮传。通判掌米盐。其为任至卑屑也。王考尝重忤当路。为其所修郤。故以是绌而困之。今评事固兵使一幕官也而自 先朝重其选。必妙简近臣之负一时峻望者以畀之。实兼弹压咨度之权。官虽卑而其责甚重。夫以我王考之冠冕一世。而犹不免挫揠斥奔。处非其地。则况汝之眇末而膺玆选任。于汝可谓荣矣。奚暇论驱驰之远。羁旅之苦哉。前此为是任者。 朝家以其有病母许改者相续也。汝亦有母病。积年阽危。常懔懔朝夕。此固同朝之所通知。 圣上亦尝有有病亲勿遣之命。而汝独不得免焉。知旧多以此为言。而顾亦有不然者。王考之赴北也。上有二尊人在堂。年龄且高。所后母李夫人惟王考是依。其情理可谓切矣。余少侍王考。尝言吾之衰白太早。由于离亲远游之多时也。以王考情理之如此。而犹割慈远赴。汝既策名登朝。身非我有。则何敢以此为辞乎。今
命。即出为高山驿丞。实万历壬寅岁也。翌年。坐事罢归。越二年乙巳。又出为镜城通判。又䠯年而罢。今汝亦以吏部郎。承 命廉察岭南。还 朝才数月。而旋出为北营评事。汝之年过王考高山时二岁而不及镜城时仅一岁耳。事若有相符者。亦异矣。然驿丞职邮传。通判掌米盐。其为任至卑屑也。王考尝重忤当路。为其所修郤。故以是绌而困之。今评事固兵使一幕官也而自 先朝重其选。必妙简近臣之负一时峻望者以畀之。实兼弹压咨度之权。官虽卑而其责甚重。夫以我王考之冠冕一世。而犹不免挫揠斥奔。处非其地。则况汝之眇末而膺玆选任。于汝可谓荣矣。奚暇论驱驰之远。羁旅之苦哉。前此为是任者。 朝家以其有病母许改者相续也。汝亦有母病。积年阽危。常懔懔朝夕。此固同朝之所通知。 圣上亦尝有有病亲勿遣之命。而汝独不得免焉。知旧多以此为言。而顾亦有不然者。王考之赴北也。上有二尊人在堂。年龄且高。所后母李夫人惟王考是依。其情理可谓切矣。余少侍王考。尝言吾之衰白太早。由于离亲远游之多时也。以王考情理之如此。而犹割慈远赴。汝既策名登朝。身非我有。则何敢以此为辞乎。今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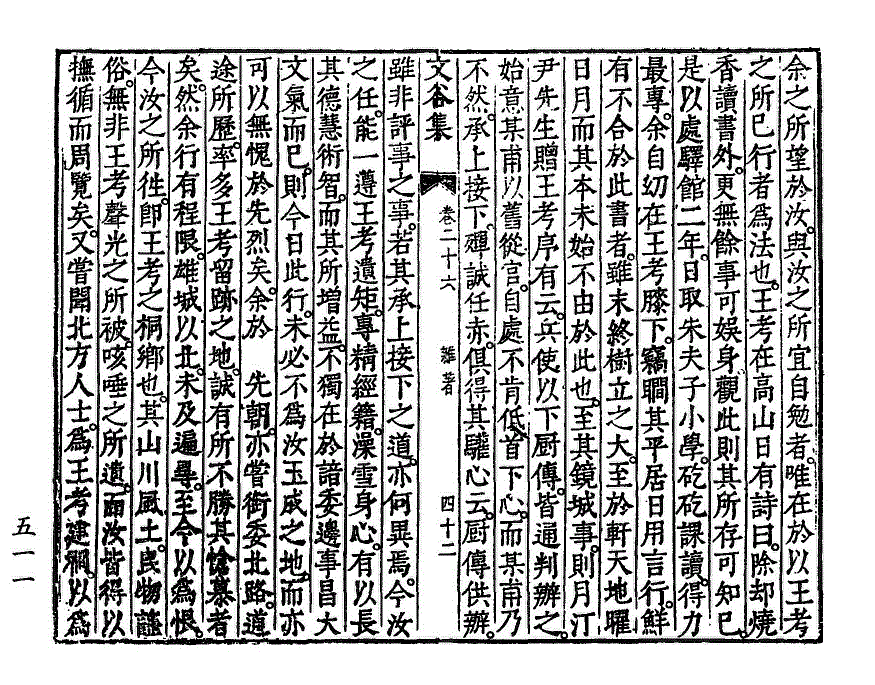 余之所望于汝。与汝之所宜自勉者。唯在于以王考之所已行者为法也。王考在高山日有诗曰。除却烧香读书外。更无馀事可娱身。观此则其所存可知已。是以处驿馆二年。日取朱夫子小学。矻矻课读。得力最专。余自幼在王考膝下。窃瞯其平居日用言行。鲜有不合于此书者。虽末终树立之大。至于轩天地曜日月而其本未始不由于此也。至其镜城事。则月汀尹先生赠王考序有云。兵使以下厨传。皆通判办之。始意某甫以旧从宫。自处不肯低首下心。而某甫乃不然。承上接下。殚诚任赤。俱得其驩心云。厨传供办。虽非评事之事。若其承上接下之道。亦何异焉。今汝之任。能一遵王考遗矩。专精经籍。澡雪身心。有以长其德慧术智。而其所增益。不独在于谙委边事昌大文气而已。则今日此行。未必不为汝玉成之地。而亦可以无愧于先烈矣。余于 先朝。亦尝衔委北路。道途所历。率多王考留迹之地。诚有所不胜其怆慕者矣。然余行有程限。雄城以北。未及遍寻。至今以为恨。今汝之所往。即王考之桐乡也。其山川风土。民物谣俗。无非王考声光之所被。咳唾之所遗。而汝皆得以抚循而周览矣。又尝闻北方人士。为王考建祠。以为
余之所望于汝。与汝之所宜自勉者。唯在于以王考之所已行者为法也。王考在高山日有诗曰。除却烧香读书外。更无馀事可娱身。观此则其所存可知已。是以处驿馆二年。日取朱夫子小学。矻矻课读。得力最专。余自幼在王考膝下。窃瞯其平居日用言行。鲜有不合于此书者。虽末终树立之大。至于轩天地曜日月而其本未始不由于此也。至其镜城事。则月汀尹先生赠王考序有云。兵使以下厨传。皆通判办之。始意某甫以旧从宫。自处不肯低首下心。而某甫乃不然。承上接下。殚诚任赤。俱得其驩心云。厨传供办。虽非评事之事。若其承上接下之道。亦何异焉。今汝之任。能一遵王考遗矩。专精经籍。澡雪身心。有以长其德慧术智。而其所增益。不独在于谙委边事昌大文气而已。则今日此行。未必不为汝玉成之地。而亦可以无愧于先烈矣。余于 先朝。亦尝衔委北路。道途所历。率多王考留迹之地。诚有所不胜其怆慕者矣。然余行有程限。雄城以北。未及遍寻。至今以为恨。今汝之所往。即王考之桐乡也。其山川风土。民物谣俗。无非王考声光之所被。咳唾之所遗。而汝皆得以抚循而周览矣。又尝闻北方人士。为王考建祠。以为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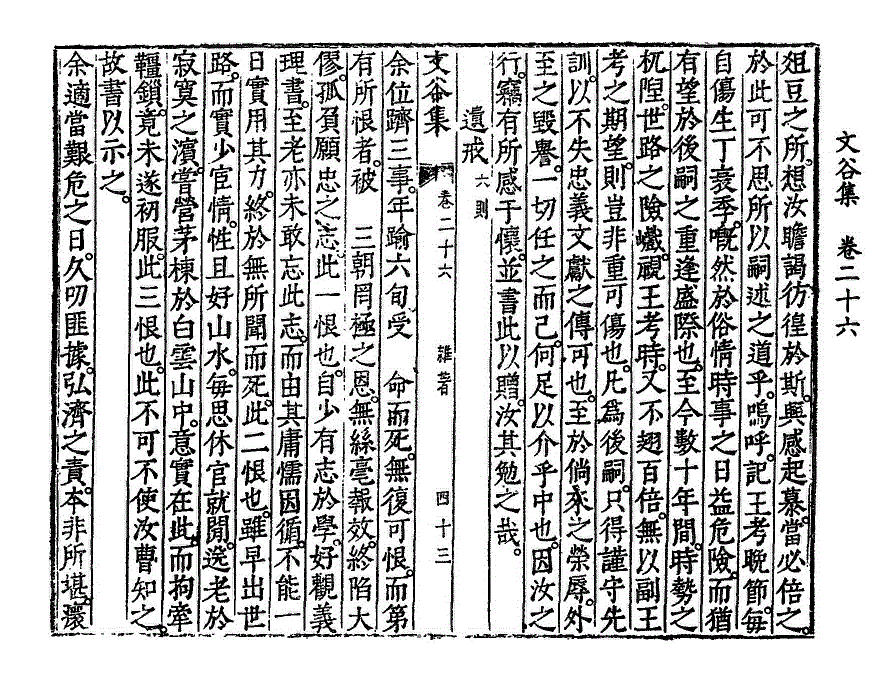 俎豆之所。想汝瞻谒彷徨于斯。兴感起慕。当必倍之。于此可不思所以嗣述之道乎。呜呼。记王考晚节。每自伤生丁衰季。嘅然于俗情时事之日益危险。而犹有望于后嗣之重逢盛际也。至今数十年间。时势之杌隉。世路之险巇。视王考时。又不翅百倍。无以副王考之期望。则岂非重可伤也。凡为后嗣。只得谨守先训。以不失忠义文献之传可也。至于倘来之荣辱。外至之毁誉。一切任之而已。何足以介乎中也。因汝之行。窃有所感于怀。并书此以赠。汝其勉之哉。
俎豆之所。想汝瞻谒彷徨于斯。兴感起慕。当必倍之。于此可不思所以嗣述之道乎。呜呼。记王考晚节。每自伤生丁衰季。嘅然于俗情时事之日益危险。而犹有望于后嗣之重逢盛际也。至今数十年间。时势之杌隉。世路之险巇。视王考时。又不翅百倍。无以副王考之期望。则岂非重可伤也。凡为后嗣。只得谨守先训。以不失忠义文献之传可也。至于倘来之荣辱。外至之毁誉。一切任之而已。何足以介乎中也。因汝之行。窃有所感于怀。并书此以赠。汝其勉之哉。遗戒(六则)
余位跻三事。年踰六旬。受 命而死。无复可恨。而第有所恨者。被 三朝罔极之恩。无丝毫报效。终陷大僇。孤负愿忠之志。此一恨也。自少有志于学。好观义理书。至老亦未敢忘此志。而由其庸懦因循。不能一日实用其力。终于无所闻而死。此二恨也。虽早出世路。而实少宦情。性且好山水。每思休官就閒。送老于寂寞之滨。尝营茅栋于白云山中。意实在此。而拘牵缰锁。竟未遂初服。此三恨也。此不可不使汝曹知之。故书以示之。
余适当艰危之日。久叨匪据。弘济之责。本非所堪。瘝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2L 页
 官病 国之罪。固不可胜赎。而若其爱 君一念。自谓可质神鬼。及至今日。区区此心。亦无以自白。唯当祈知于后世之子云耳。
官病 国之罪。固不可胜赎。而若其爱 君一念。自谓可质神鬼。及至今日。区区此心。亦无以自白。唯当祈知于后世之子云耳。先祖考临终。尝以丧祭从俭有遗戒。余之无状。固不及先祖万一。而况今得罪 君父。忝累先德。尤不可自同无故之人。丧祭凡事。务从俭约。毋得少有踰滥。以遵余此志。
吾家丧祭之礼。有违于古礼者颇多。先祖考每以先世行之既久。难于率意釐改为教。而亦尝有其中不可不改者。则后孙可以量度而改之之教矣。凡事久则当变。不可一向胶守。今余之丧。丧祭诸礼。除古今异宜财力不逮者外。一从丧礼备要以行之。
墓道石役。固不宜过为侈大。以效弊习。而先祖考神道。亦因治命。不得立碑。今余之墓。只树短表。且埋志石。略记世系生卒履历。毋得张皇文字。以取人讥笑。余素无才德。徒以凭藉先荫。厚蒙 国恩。窃位踰分。自速衅孽。今日之事。无非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于此。虽悔曷及。凡我子孙。宜以我为戒。常存谦退之志。仕宦则避远显要。居家则力行恭俭。至于慎交游简言议。一遵先世遗矩。以为褆身保家之地。至佳至
文谷集卷之二十六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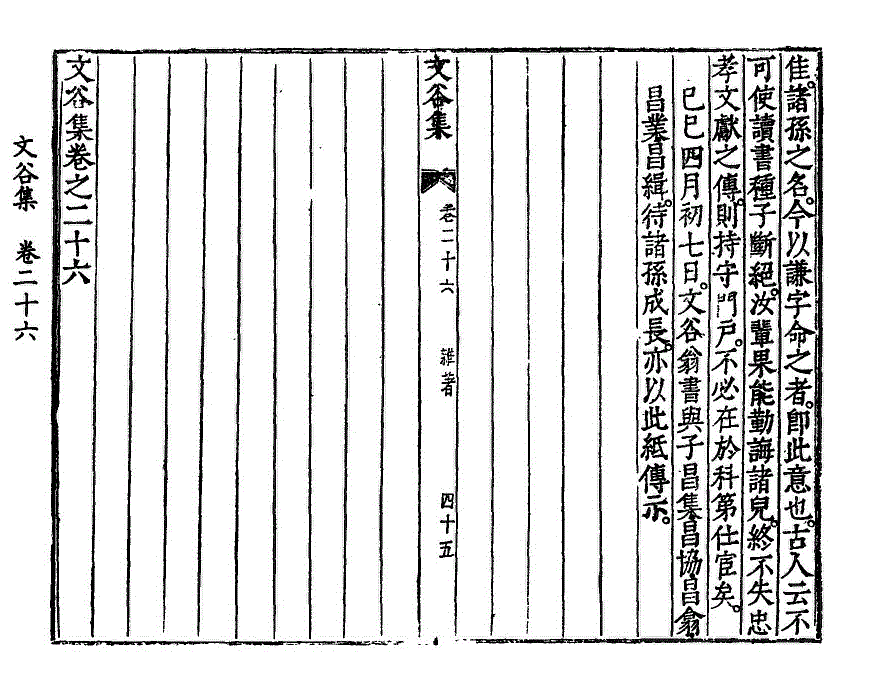 隹。诸孙之名。今以谦字命之者。即此意也。古人云不可使读书种子断绝。汝辈果能勤诲诸儿。终不失忠孝文献之传。则持守门户。不必在于科第仕宦矣。
隹。诸孙之名。今以谦字命之者。即此意也。古人云不可使读书种子断绝。汝辈果能勤诲诸儿。终不失忠孝文献之传。则持守门户。不必在于科第仕宦矣。己巳四月初七日。文谷翁书与子昌集,昌协,昌翕,昌业,昌缉。待诸孙成长。亦以此纸传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