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x 页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杂著○复雠说[下]
杂著○复雠说[下]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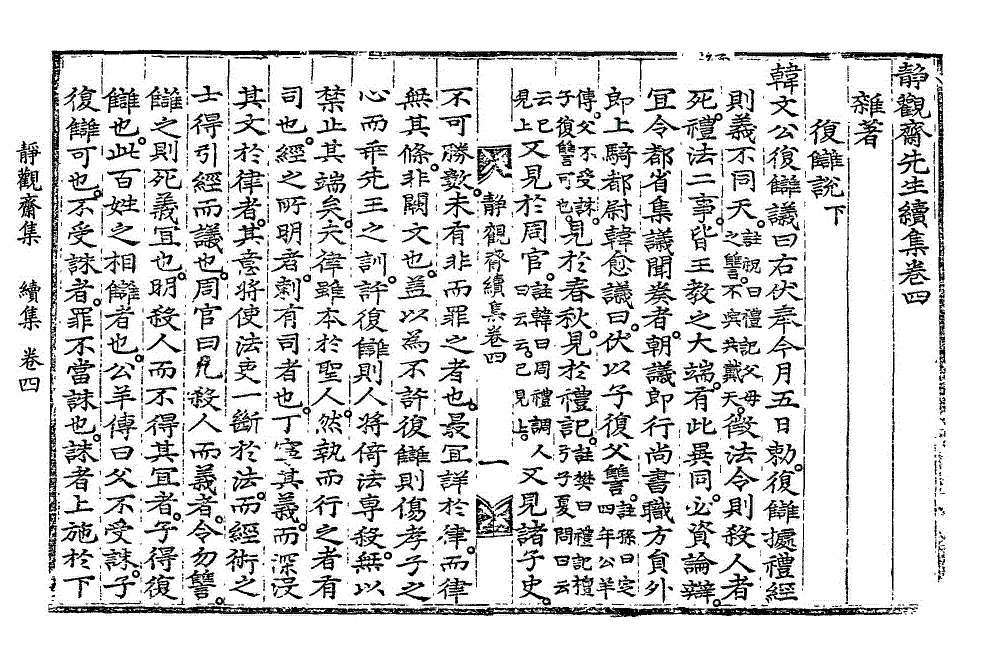 [韩文公复雠议]
[韩文公复雠议]韩文公复雠议曰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雠据礼经则义不同天。(注祝曰礼记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徵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伏以子复父雠。(注孙曰定四年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见于春秋。见于礼记。(注樊曰礼记檀弓子夏问曰云云已见上)又见于周官。(注韩曰周礼调人曰云云。已见上)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则伤考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雠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刺有司者也。丁宁其义。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雠也。此百姓之相雠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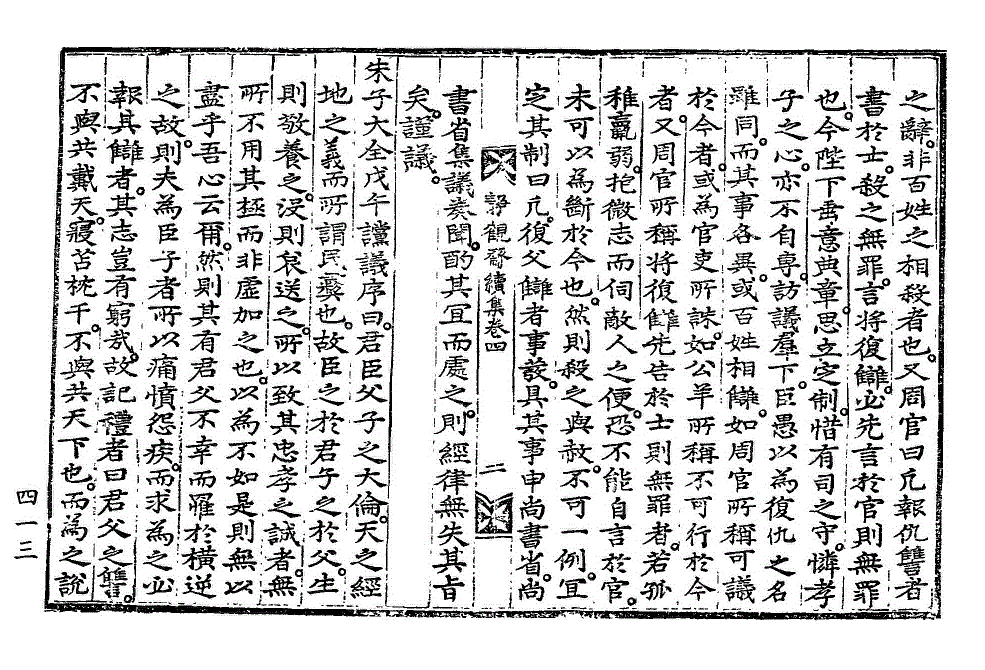 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雠。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亦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谨议。
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雠。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亦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谨议。[朱子大全戊午谠议序]
朱子大全戊午谠议序曰。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尽乎吾心云尔。然则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夫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雠者。其志岂有穷哉。故记礼者曰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为之说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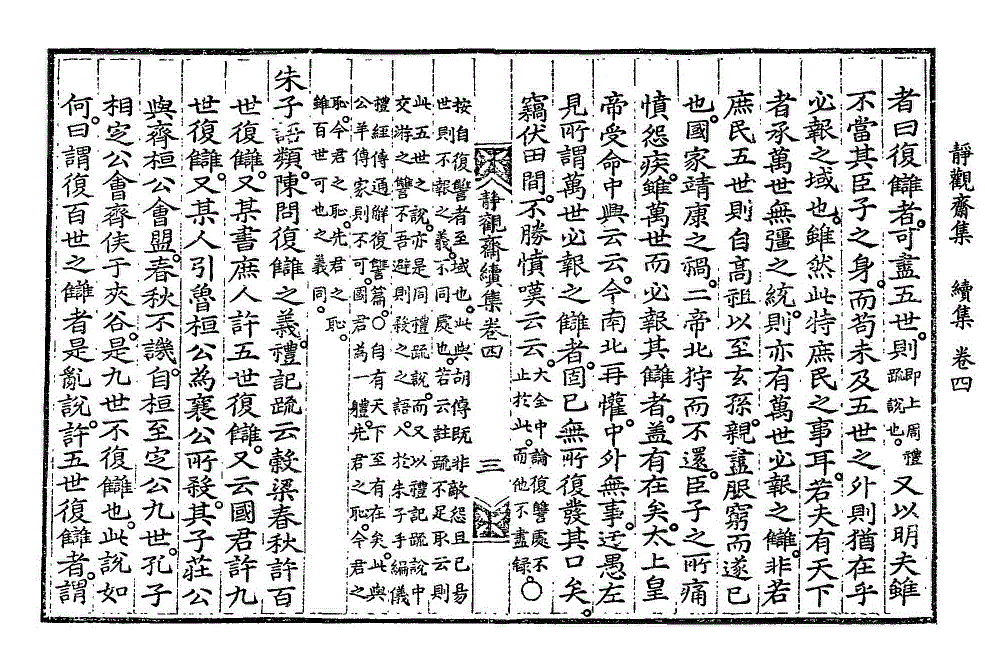 者曰复雠者。可尽五世。则(即上周礼疏说也。)又以明夫虽不当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则犹在乎必报之域也。虽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彊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雠者。盖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兴云云。今南北再欢。中外无事。迂愚左见所谓万世必报之雠者。固已无所复发其口矣。窃伏田间。不胜愤叹云云。(大全中论复雠处不止于此。而他不尽录。○按自复雠者至域也。此与胡传既非敌怨且已易世则不报之义。不同处也。若云注疏不足取云则此五世之说。亦是周礼疏说。而又以礼记疏说中交游之雠不吾避则杀之之语。入于朱子手编仪礼经传通解复雠篇。○自有天下至有在矣。此与公羊传家则不可。国君为一体。先君之耻。今君之耻。今君之耻。先君之耻。虽百世可也之义同。)
者曰复雠者。可尽五世。则(即上周礼疏说也。)又以明夫虽不当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则犹在乎必报之域也。虽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彊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雠者。盖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兴云云。今南北再欢。中外无事。迂愚左见所谓万世必报之雠者。固已无所复发其口矣。窃伏田间。不胜愤叹云云。(大全中论复雠处不止于此。而他不尽录。○按自复雠者至域也。此与胡传既非敌怨且已易世则不报之义。不同处也。若云注疏不足取云则此五世之说。亦是周礼疏说。而又以礼记疏说中交游之雠不吾避则杀之之语。入于朱子手编仪礼经传通解复雠篇。○自有天下至有在矣。此与公羊传家则不可。国君为一体。先君之耻。今君之耻。今君之耻。先君之耻。虽百世可也之义同。)[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陈问复雠之义。礼记疏云谷梁春秋许百世复雠。又某书庶人许五世复雠。又云国君许九世复雠。又某人引鲁桓公为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会盟。春秋不讥。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是九世不复雠也。此说如何。曰谓复百世之雠者是乱说。许五世复雠者。谓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4L 页
 亲亲之恩。欲至五世而斩也。春秋许九世复雠与春秋不讥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乱说。春秋何尝说不讥与美他来。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后世言春秋者动引讥美为言。不知他何从见圣人讥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样。国君复雠之事又不同。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祸。虽百世复之可也。曰这事难说。久之曰凡事贵谋始也。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鲁庄公之事。他亲见齐襄公杀其父。既不能复。又亲与之燕会。又与之主婚。筑王姬之馆于东门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为如此。岂特不能复而已。既亲与雠人如此。如何更责他报齐桓公。况更欲责定公夹谷之会。争那里去。见雠在面前。不曾报得。更欲报之于其子若孙。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没气势无意思了。又况齐桓公率诸侯尊周室。以义而举。庄公虽欲不赴其盟会。岂可得哉。事又当权个时势义理轻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无事自来召诸侯。如此则庄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为尊王室。若庄公不赴。非是叛齐。乃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气势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复得雠。若欲复雠则
亲亲之恩。欲至五世而斩也。春秋许九世复雠与春秋不讥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乱说。春秋何尝说不讥与美他来。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后世言春秋者动引讥美为言。不知他何从见圣人讥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样。国君复雠之事又不同。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祸。虽百世复之可也。曰这事难说。久之曰凡事贵谋始也。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鲁庄公之事。他亲见齐襄公杀其父。既不能复。又亲与之燕会。又与之主婚。筑王姬之馆于东门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为如此。岂特不能复而已。既亲与雠人如此。如何更责他报齐桓公。况更欲责定公夹谷之会。争那里去。见雠在面前。不曾报得。更欲报之于其子若孙。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没气势无意思了。又况齐桓公率诸侯尊周室。以义而举。庄公虽欲不赴其盟会。岂可得哉。事又当权个时势义理轻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无事自来召诸侯。如此则庄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为尊王室。若庄公不赴。非是叛齐。乃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气势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复得雠。若欲复雠则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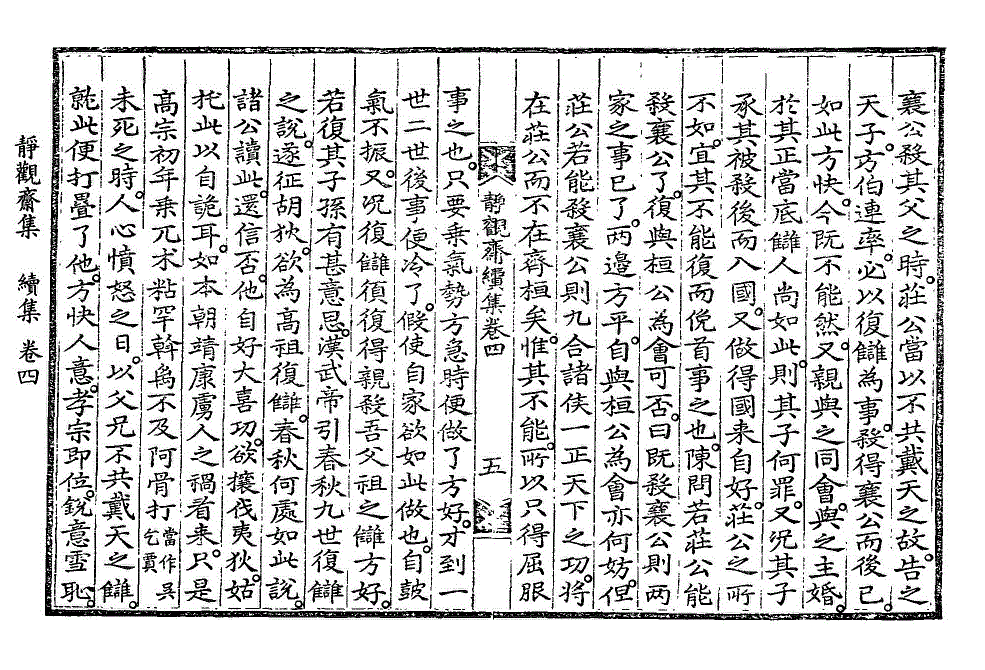 襄公杀其父之时。庄公当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连率。必以复雠为事。杀得襄公而后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亲与之同会。与之主婚。于其正当底雠人尚如此。则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杀后而入国。又做得国来自好。庄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复而俛首事之也。陈问若庄公能杀襄公了。复与桓公为会可否。曰既杀襄公则两家之事已了。两边方平。自与桓公为会亦何妨。但庄公若能杀襄公则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之功。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气势方急时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后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气不振。又况复雠须复得亲杀吾父祖之雠方好。若复其子孙有甚意思。汉武帝引春秋九世复雠之说。遂征胡狄。欲为高祖复雠。春秋何处如此说。诸公读此。还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诡耳。如本朝靖康虏人之祸看来。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当作吴乞贾)未死之时。人心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雠。就此便打叠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锐意雪耻。
襄公杀其父之时。庄公当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连率。必以复雠为事。杀得襄公而后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亲与之同会。与之主婚。于其正当底雠人尚如此。则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杀后而入国。又做得国来自好。庄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复而俛首事之也。陈问若庄公能杀襄公了。复与桓公为会可否。曰既杀襄公则两家之事已了。两边方平。自与桓公为会亦何妨。但庄公若能杀襄公则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之功。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气势方急时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后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气不振。又况复雠须复得亲杀吾父祖之雠方好。若复其子孙有甚意思。汉武帝引春秋九世复雠之说。遂征胡狄。欲为高祖复雠。春秋何处如此说。诸公读此。还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诡耳。如本朝靖康虏人之祸看来。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当作吴乞贾)未死之时。人心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雠。就此便打叠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锐意雪耻。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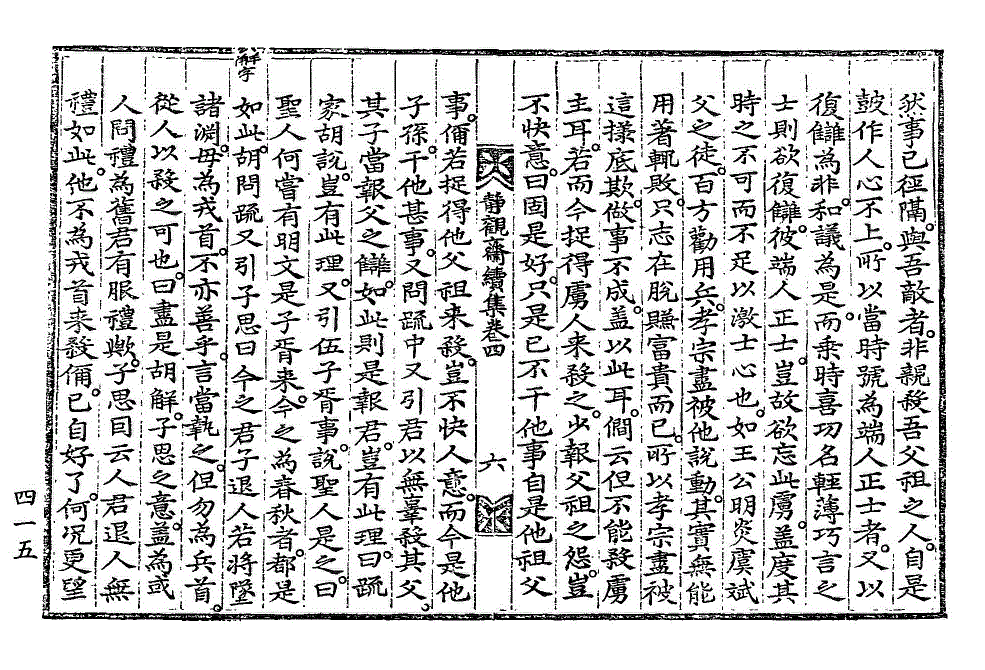 然事已径隔。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当时号为端人正士者。又以复雠为非。和议为是。而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雠。彼端人正士。岂故欲忘此虏。盖度其时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劝用兵。孝宗尽被他说动。其实无能用著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所以孝宗尽被这样底欺。做事不成。盖以此耳。僩云但不能杀虏主耳。若而今捉得虏人来杀之。少报父祖之怨。岂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来杀。岂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孙。干他甚事。又问疏中又引君以无辜杀其父。其子当报父之雠。如此则是报君。岂有此理。曰疏家胡说。岂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说圣人是之。曰圣人何尝有明文是子胥来。今之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问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言当执之。但勿为兵首。从人以杀之可也。曰尽是胡解。子思之意。盖为或人问礼为旧君有服礼欤。子思因云人君退人无礼如此。他不为戎首来杀你。已自好了。何况更望
然事已径隔。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当时号为端人正士者。又以复雠为非。和议为是。而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雠。彼端人正士。岂故欲忘此虏。盖度其时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劝用兵。孝宗尽被他说动。其实无能用著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所以孝宗尽被这样底欺。做事不成。盖以此耳。僩云但不能杀虏主耳。若而今捉得虏人来杀之。少报父祖之怨。岂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来杀。岂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孙。干他甚事。又问疏中又引君以无辜杀其父。其子当报父之雠。如此则是报君。岂有此理。曰疏家胡说。岂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说圣人是之。曰圣人何尝有明文是子胥来。今之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问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言当执之。但勿为兵首。从人以杀之可也。曰尽是胡解。子思之意。盖为或人问礼为旧君有服礼欤。子思因云人君退人无礼如此。他不为戎首来杀你。已自好了。何况更望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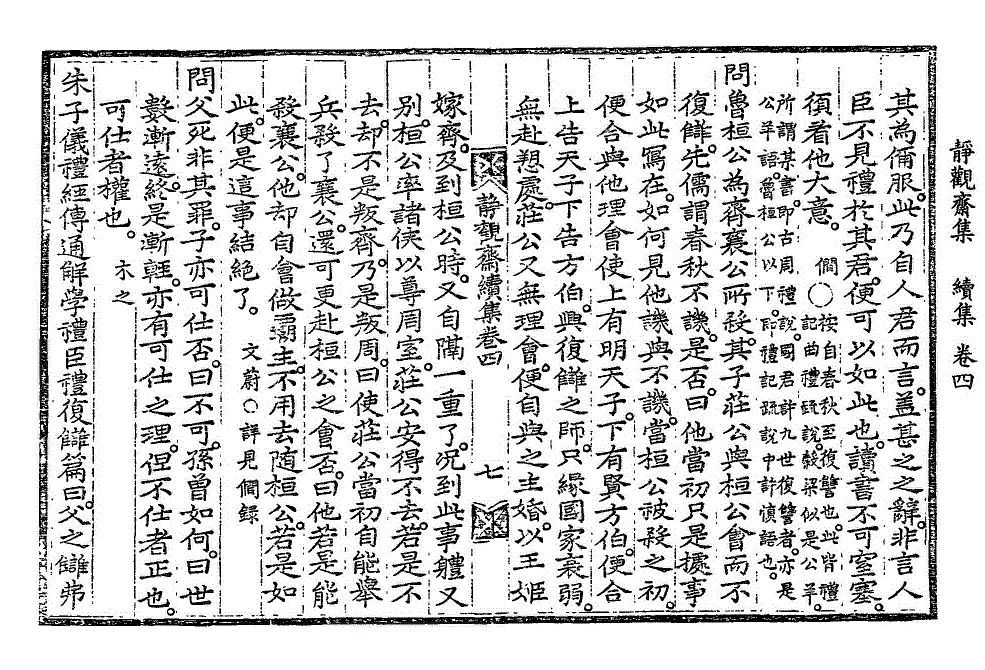 其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盖甚之之辞。非言人臣不见礼于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读书不可窒塞。须看他大意。(僩)○(按自春秋至复雠也。此皆礼记曲礼疏说。谷梁似是公羊。所谓某书。即古周礼说。国君许九世复雠者。亦是公羊语。鲁桓公以下。即礼记疏说中许慎语也。)
其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盖甚之之辞。非言人臣不见礼于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读书不可窒塞。须看他大意。(僩)○(按自春秋至复雠也。此皆礼记曲礼疏说。谷梁似是公羊。所谓某书。即古周礼说。国君许九世复雠者。亦是公羊语。鲁桓公以下。即礼记疏说中许慎语也。)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而不复雠。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据事如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合与他理会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雠之师。只缘国家衰弱。无赴愬处。庄公又无理会。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曰使庄公当初自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更赴桓公之会否。曰他若是能杀襄公。他却自会做霸主。不用去随桓公。若是如此。便是这事结绝了。(文蔚○详见僩录)
问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孙曾如何。曰世数渐远。终是渐轻。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权也。(木之)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学礼臣礼复雠篇]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学礼臣礼复雠篇曰。父之雠弗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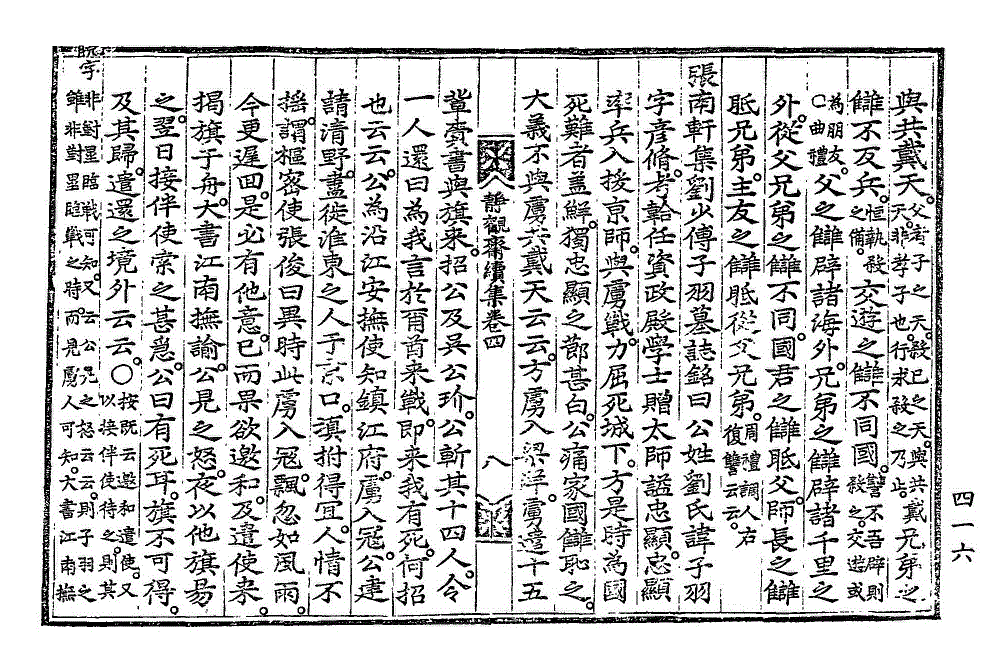 与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兄弟之雠不反兵。(恒执杀之备。)交游之雠不同国。(雠不吾辟则杀之。交游或为朋友。○曲礼)父之雠辟诸海外。兄弟之雠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雠不同。国君之雠视父。师长之雠视兄弟。主友之雠视从父兄弟。(周礼调人右复雠云云。)
与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兄弟之雠不反兵。(恒执杀之备。)交游之雠不同国。(雠不吾辟则杀之。交游或为朋友。○曲礼)父之雠辟诸海外。兄弟之雠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雠不同。国君之雠视父。师长之雠视兄弟。主友之雠视从父兄弟。(周礼调人右复雠云云。)[张南轩集刘少傅子羽墓志铭]
张南轩集刘少傅子羽墓志铭曰公姓刘氏讳子羽字彦脩。考韐任资政殿学士赠太师谥忠显。忠显率兵入援京师。与虏战。力屈死城下。方是时为国死难者盖鲜。独忠显之节甚白。公痛家国雠耻之。大义不与虏共戴天云云。方虏入梁洋。虏遣十五辈赍书与旗来。招公及吴公玠。公斩其十四人。令一人还曰为我言于尔酋来战。即来我有死。何招也云云。公为沿江安抚使知镇江府。虏入寇。公建请清野。尽徙淮东之人于京口。滇拊得宜。人情不摇。谓枢密使张俊曰异时此虏入寇。飘忽如风雨。今更迟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来。揭旗于舟。大书江南抚谕。公见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及其归。遣还之境外云云。○(按既云邀和遣使。又以接伴使待之。则其非对垒临战可知。又云公见之怒云云。则子羽之虽非对垒临战之时。而见虏人可知。大书江南抚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7H 页
 谕见之怒。有死耳。旗不可得。遣还之境外云。则其怒以易之。乃以江南抚谕四字故也。非以父雠之故而然也。子羽是欲报君父之雠者。非只为亲雠者也。)
谕见之怒。有死耳。旗不可得。遣还之境外云。则其怒以易之。乃以江南抚谕四字故也。非以父雠之故而然也。子羽是欲报君父之雠者。非只为亲雠者也。)[朱子大全刘少傅子羽神道碑]
朱子大全刘少傅子羽神道碑曰。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观文殿学士彭城刘侯珙薨于建康之府舍。疾革时手为书授其弟玶。使以属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盖犹有待也。今家国之雠未报。而珙衔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发书恸哭曰。呜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早失吾父。少傅公实收教之。共父之责乃吾责也。即访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状。又得今江陵张侯栻所为铭。以次其事曰。公姓刘氏讳子羽字某云云。在镇江。会金虏复渝盟。公建议清野。尽徙淮东之人于京口。抚以威信。兵民杂居。无敢相侵扰者云云。既而虏骑久不至。枢密使张俊视师江上。以问公。公曰此虏异时入寇。飘忽如风雨。今更迟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复以和为请。使至植大旗舟上。书曰江南抚谕。公见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见旗有异。大惧索之急。公曰吾为守臣。朝论无所与。然欲揭此于吾州之境则吾有死而已。索犹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云云。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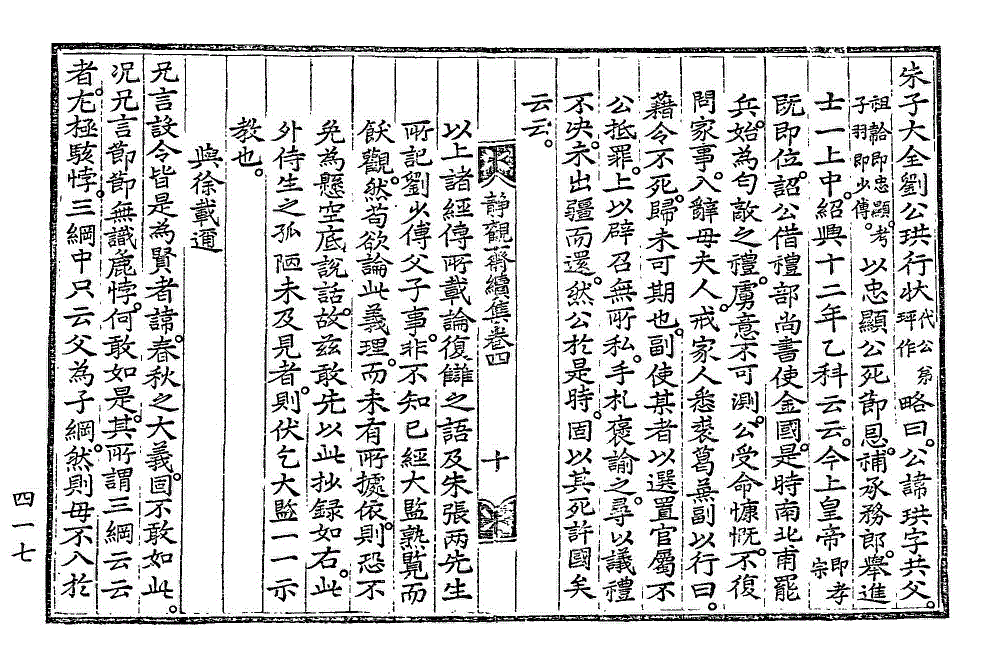 [朱子大全刘公珙行状]
[朱子大全刘公珙行状]朱子大全刘公珙行状(代公弟玶作)略曰。公讳珙字共父。(祖韐即忠显。考子羽即少傅。)以忠显公死节恩。补承务郎。举进士一上中。绍兴十二年乙科云云。今上皇帝(即孝宗)既即位。诏公借礼部尚书使金国。是时南北甫罢兵。始为匀敌之礼。虏意不可测。公受命慷慨。不复问家事。入辞母夫人。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归未可期也。副使某者以选置官属不公抵罪。上以辟召无所私。手札褒谕之。寻以议礼不决。未出疆而还。然公于是时。固以其死许国矣云云。
以上诸经传所载论复雠之语及朱张两先生所记刘少傅父子事。非不知已经大监熟览而饫观。然苟欲论此义理。而未有所据依。则恐不免为悬空底说话。故兹敢先以此抄录如右。此外侍生之孤陋未及见者。则伏乞大监一一示教也。
与徐载迩
兄言设令皆是为贤者讳。春秋之大义。固不敢如此。况兄言节节无识粗悖。何敢如是。其所谓三纲云云者。尤极骇悖。三纲中只云父为子纲。然则母不入于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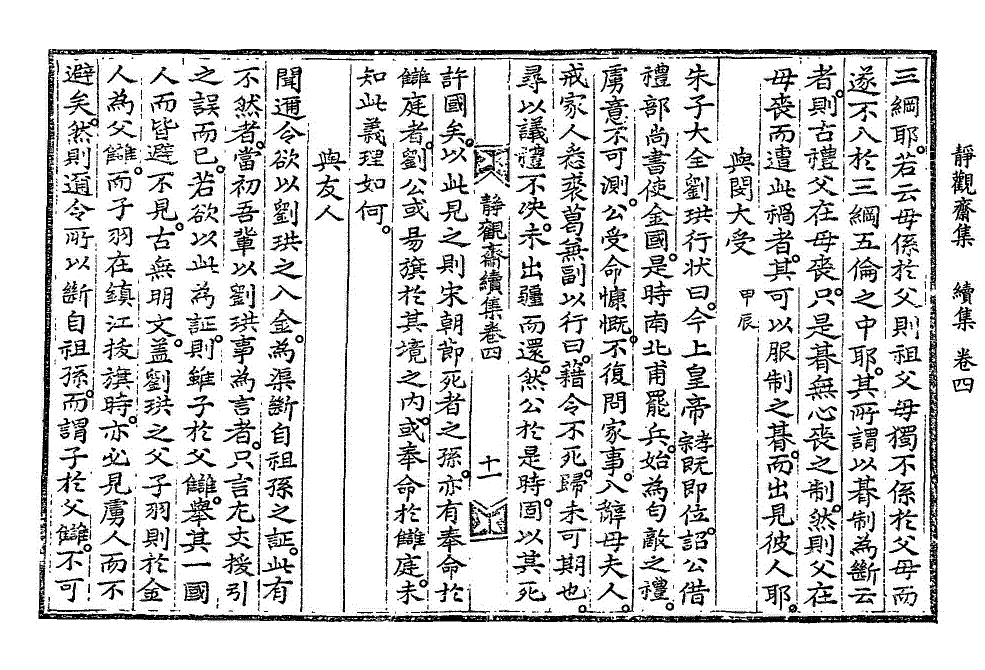 三纲耶。若云母系于父则祖父母独不系于父母而遂不入于三纲五伦之中耶。其所谓以期制为断云者。则古礼父在母丧。只是期无心丧之制。然则父在母丧而遭此祸者。其可以服制之期。而出见彼人耶。
三纲耶。若云母系于父则祖父母独不系于父母而遂不入于三纲五伦之中耶。其所谓以期制为断云者。则古礼父在母丧。只是期无心丧之制。然则父在母丧而遭此祸者。其可以服制之期。而出见彼人耶。与闵大受(甲辰)
朱子大全刘珙行状曰。今上皇帝(孝宗)既即位。诏公借礼部尚书使金国。是时南北甫罢兵。始为匀敌之礼。虏意不可测。公受命慷慨。不复问家事。入辞母夫人。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归未可期也。寻以议礼不决。未出疆而还。然公于是时。固以其死许国矣。以此见之则宋朝节死者之孙。亦有奉命于雠庭者。刘公或易旗于其境之内。或奉命于雠庭。未知此义理如何。
与友人
闻迩令欲以刘珙之入金。为渠断自祖孙之證。此有不然者。当初吾辈以刘珙事为言者。只言尤丈援引之误而已。若欲以此为證。则虽子于父雠。举其一国人而皆避不见。古无明文。盖刘珙之父子羽则于金人为父雠。而子羽在镇江拔旗时。亦必见虏人而不避矣。然则迩令所以断自祖孙。而谓子于父雠。不可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8L 页
 不举其国之人而皆不可见云者。是何所据。只以三纲为言则母将不入于三纲之中。亦将奈何。迩令若必以刘珙事为證而更是前见。则恐不免又起士论之大闹矣。
不举其国之人而皆不可见云者。是何所据。只以三纲为言则母将不入于三纲之中。亦将奈何。迩令若必以刘珙事为證而更是前见。则恐不免又起士论之大闹矣。答金起之(甲辰)
顷者久令有书问之语。故未免破戒走草以送。语多未莹者。槩弟意元不出身从仕之人则虽上过五代祖下至朋友之雠。诚可以伸其私义。既出而从仕之后。便欲与父母祖父母之雠。混谓私义无轻重。皆不出见。全没公义一边则岂有此理也。尤丈之意。必不如此。而向来峻论者只知怒迩令无识粗悖。便谓义理如此。尤丈之意亦如此。遂以周礼中相反之语。入于儒疏中而浑沦为说。此极可笑。迩令之粗悖无识固极矣。公论之如是峻斥。诚无足怪。而此一款义理。岂有如此之理。尤丈之意亦岂如此也。然则终不可无一处限制之意。不可谓全非也。详见三礼疏说则亦可以傍照参看而知之。哓哓之说。固不足挂之齿颊。而如季明诸人亦未免为某人辈所眩惑云。极可叹也。
答金久之(甲辰○见原集)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9H 页
 附答书
附答书别纸示谕。明白洞析。无复遗蕴。令人洒然。以五世复雠为不可云者。苟非丧心之人。岂有此论。今之谤兄者。不能舒究义理曲折。而唯哓哓之是事。此不足挂齿。亦何必多辨也。至于五代祖以下至从昆弟朋友有雠之义者。皆不可见彼人干彼事云者。弟虽不知礼经义理之如何。决是必不行之事。亦是必不然之理也。未知尤丈所答以为如何也。
甲辰疏语
顷年时烈以意外之事。苍黄退去。其后又以当初服制议礼之事。继有善道之疏。时烈服制之论。上据周公之经训。正正堂堂。诚可谓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而其后赵絅,洪宇远,赵寿益等诸人之疏相继而起。及至顷日。又以金万均之事。遽有徐必远之疏。当初时烈疏意。只欲以朱夫子戊午谠议序中之语。立大防于一世。明大义于天下。以救渐溺之人心。晓此义理于上下而已。至若因此必欲一依礼经所载而行之于今日。亦不无似同而异者。古今异宜。时势不同。其间岂可无斟量之道也。以此言之则必远之断自祖孙者。果为无识。其所谓不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19L 页
 可无斟量云者。则主意所在。不可谓全无所见。然其以粗厉之语。肆加讥侮于时烈者。极涉骇悖。乌得无罪。而前后之攻必远者攻之太深。亦未能得其情而使自愧服。 殿下于其间。时有显示左右者。时烈因其一疏。以致朝著之大闹。累月不已。则其心之不安势亦然矣。臣于此论。不无可避之嫌。而以其为公是公非。不得不言也。
可无斟量云者。则主意所在。不可谓全无所见。然其以粗厉之语。肆加讥侮于时烈者。极涉骇悖。乌得无罪。而前后之攻必远者攻之太深。亦未能得其情而使自愧服。 殿下于其间。时有显示左右者。时烈因其一疏。以致朝著之大闹。累月不已。则其心之不安势亦然矣。臣于此论。不无可避之嫌。而以其为公是公非。不得不言也。乙巳疏语
乃若徐必远之事则臣于其时。只以其事之已著于前后章疏者。循其序而次第历论而已。实无分寸意思。必欲专归于必远者也。若其所争之论则必远之海西疏语。只见古人一二文字之众所饫见者。便以为得其断案。遂肆无限说话。殊不知此外亦有许多古人言语可以参互援證裁量折衷于其间如韩文公之议者。此则可笑。不必多辨。亦不欲到今覼缕。以明其如何。而独恨其论臣一款。用意颇深。必远平生以朴直自许。若果怒臣至此。必欲深攻臣身。则直肆愤骂。任意丑诋。亦无不可。而乃以嘲戏侮弄之语。杂陈 君父之前。有若眩惑者然。以朴直自许之人。果如是乎。臣于此不以被其嘲侮为愧。还以必远之乃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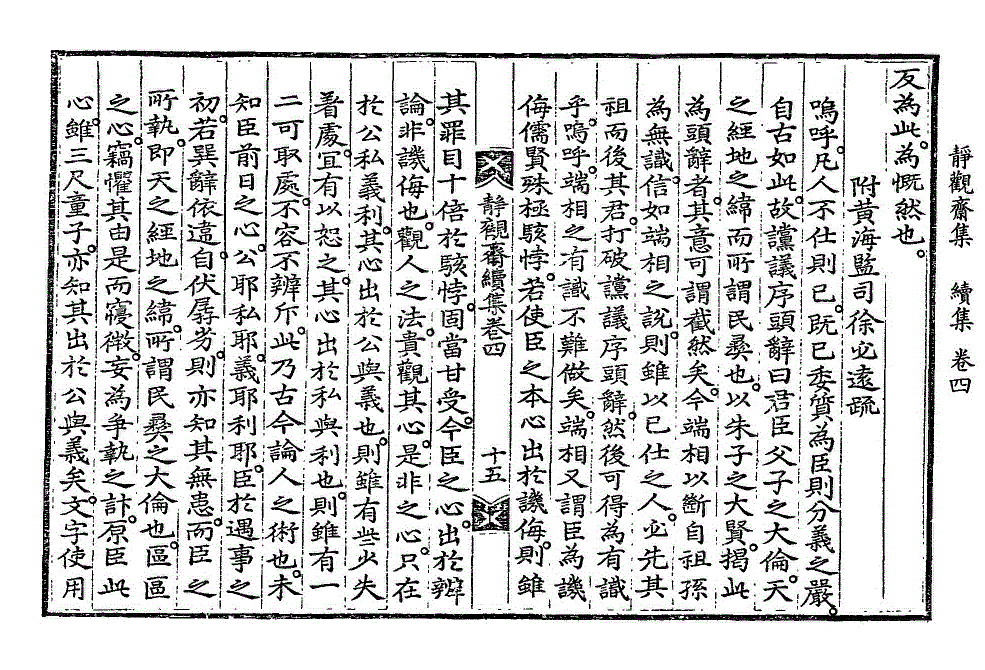 反为此。为慨然也。
反为此。为慨然也。附黄海监司徐必远疏
呜呼。凡人不仕则已。既已委质为臣则分义之严。自古如此。故谠议序头辞曰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纬而所谓民彝也。以朱子之大贤。揭此为头辞者。其意可谓截然矣。今端相以断自祖孙为无识。信如端相之说。则虽以已仕之人。必先其祖而后其君。打破谠议序头辞。然后可得为有识乎。呜呼。端相之有识不难做矣。端相又谓臣为讥侮儒贤殊极骇悖。若使臣之本心出于讥侮。则虽其罪目十倍于骇悖。固当甘受。今臣之心。出于辨论。非讥侮也。观人之法。贵观其心。是非之心。只在于公私义利。其心出于公与义也。则虽有些少失着处。宜有以恕之。其心出于私与利也。则虽有一二可取处。不容不辨斥。此乃古今论人之术也。未知臣前日之心。公耶私耶。义耶利耶。臣于遇事之初。若巽辞依违。自伏孱劣。则亦知其无患。而臣之所执。即天之经地之纬。所谓民彝之大伦也。区区之心。窃惧其由是而寝微。妄为争执之计。原臣此心。虽三尺童子。亦知其出于公与义矣。文字使用
静观斋先生续集卷四 第 4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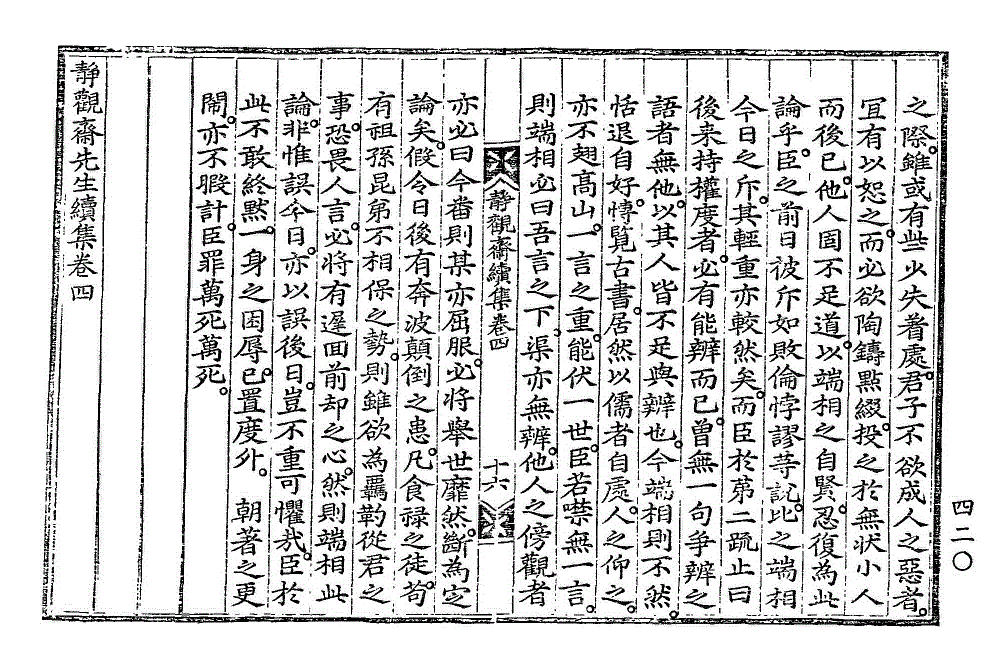 之际。虽或有些少失着处。君子不欲成人之恶者。宜有以恕之。而必欲陶铸点缀。投之于无状小人而后已。他人固不足道。以端相之自贤。忍复为此论乎。臣之前日被斥如败伦悖谬等说。比之端相今日之斥。其轻重亦较然矣。而臣于第二疏止曰后来持权度者。必有能辨而已。曾无一句争辨之语者无他。以其人皆不足与辨也。今端相则不然。恬退自好。博览古书。居然以儒者自处。人之仰之。亦不翅高山。一言之重。能伏一世。臣若噤无一言。则端相必曰吾言之下。渠亦无辨。他人之傍观者亦必曰今番则某亦屈服。必将举世靡然。断为定论矣。假令日后有奔波颠倒之患。凡食禄之徒。苟有祖孙昆弟不相保之势。则虽欲为羁靮从君之事。恐畏人言。必将有迟回前却之心。然则端相此论。非惟误今日。亦以误后日。岂不重可惧哉。臣于此不敢终默。一身之困辱。已置度外。 朝著之更闹。亦不暇计。臣罪万死万死。
之际。虽或有些少失着处。君子不欲成人之恶者。宜有以恕之。而必欲陶铸点缀。投之于无状小人而后已。他人固不足道。以端相之自贤。忍复为此论乎。臣之前日被斥如败伦悖谬等说。比之端相今日之斥。其轻重亦较然矣。而臣于第二疏止曰后来持权度者。必有能辨而已。曾无一句争辨之语者无他。以其人皆不足与辨也。今端相则不然。恬退自好。博览古书。居然以儒者自处。人之仰之。亦不翅高山。一言之重。能伏一世。臣若噤无一言。则端相必曰吾言之下。渠亦无辨。他人之傍观者亦必曰今番则某亦屈服。必将举世靡然。断为定论矣。假令日后有奔波颠倒之患。凡食禄之徒。苟有祖孙昆弟不相保之势。则虽欲为羁靮从君之事。恐畏人言。必将有迟回前却之心。然则端相此论。非惟误今日。亦以误后日。岂不重可惧哉。臣于此不敢终默。一身之困辱。已置度外。 朝著之更闹。亦不暇计。臣罪万死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