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畏斋集卷之十一
言行录
言行录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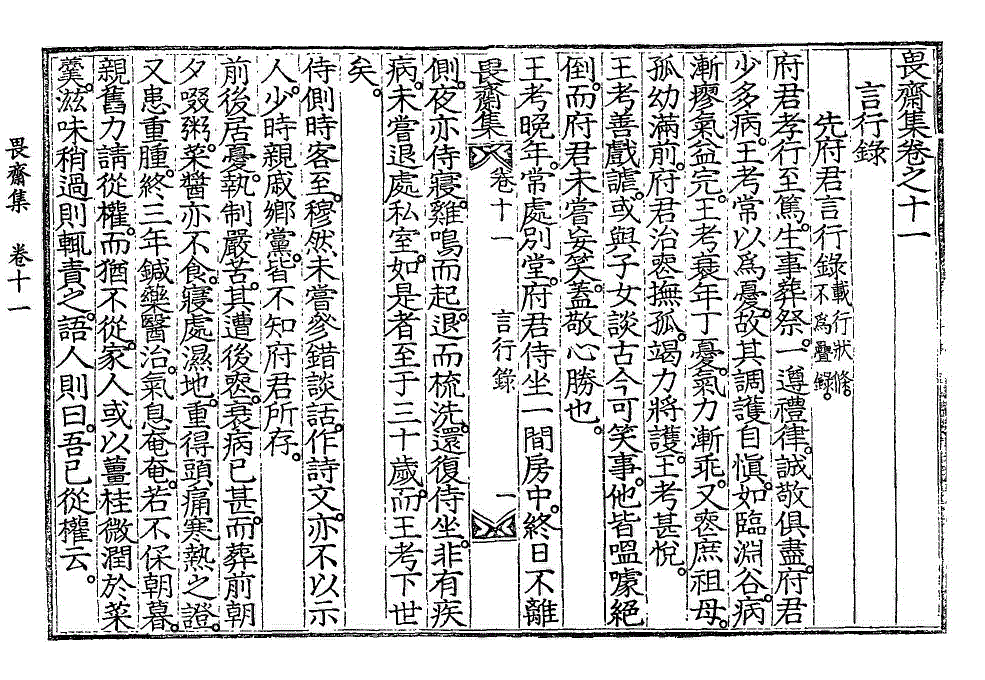 先府君言行录(载行状条。不为叠录。)
先府君言行录(载行状条。不为叠录。)府君孝行至笃。生事葬祭。一遵礼律。诚敬俱尽。府君少多病。王考常以为忧。故其调护自慎。如临渊谷。病渐瘳气益完。王考衰年丁忧。气力渐乖。又丧庶祖母。孤幼满前。府君治丧抚孤。竭力将护。王考甚悦。
王考善戏谑。或与子女谈古今可笑事。他皆嗢噱绝倒。而府君未尝妄笑。盖敬心胜也。
王考晚年。常处别堂。府君侍坐一间房中。终日不离侧。夜亦侍寝。鸡鸣而起。退而梳洗。还复侍坐。非有疾病。未尝退处私室。如是者至于三十岁。而王考下世矣。
侍侧时客至。穆然未尝参错谈话。作诗文。亦不以示人。少时亲戚乡党。皆不知府君所存。
前后居忧。执制严苦。其遭后丧。衰病已甚。而葬前朝夕啜粥。菜酱亦不食。寝处湿地。重得头痛寒热之證。又患重肿。终三年针药医治。气息奄奄。若不保朝暮。亲旧力请从权。而犹不从。家人或以姜桂微润于菜羹。滋味稍过则辄责之。语人则曰。吾已从权云。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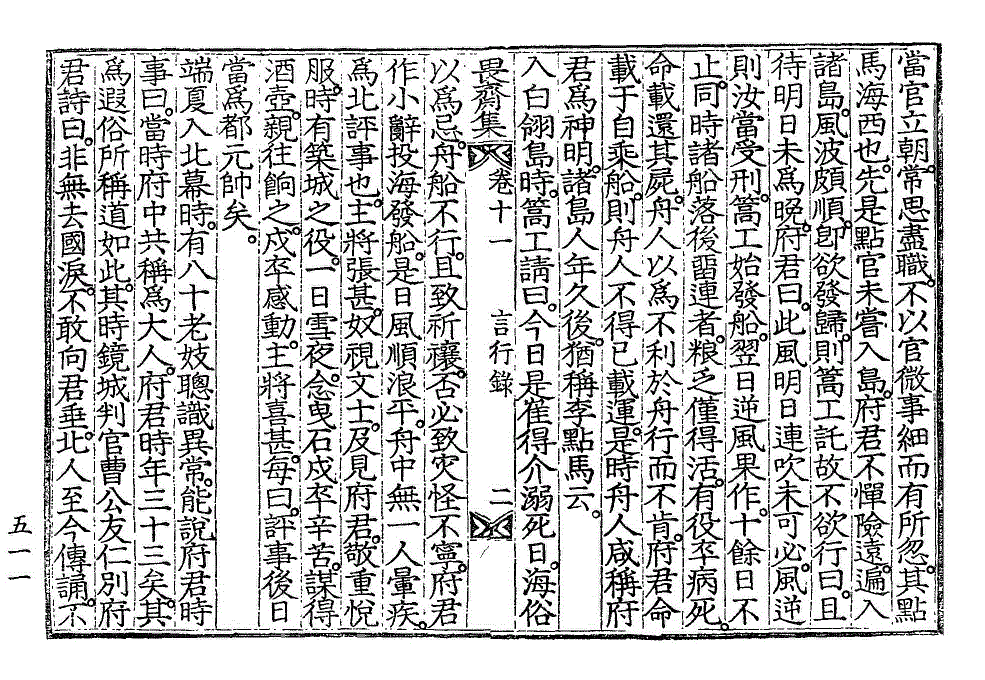 当官立朝。常思尽职。不以官微事细而有所忽。其点马海西也。先是点官未尝入岛。府君不惮险远。遍入诸岛。风波颇顺。即欲发归。则篙工托故不欲行曰。且待明日未为晚。府君曰。此风明日连吹未可必。风逆则汝当受刑。篙工始发船。翌日逆风果作。十馀日不止。同时诸船落后留连者。粮乏仅得活。有役卒病死。命载还其尸。舟人以为不利于舟行而不肯。府君命载于自乘船。则舟人不得已载运。是时舟人咸称府君为神明。诸岛人年久后。犹称李点马云。
当官立朝。常思尽职。不以官微事细而有所忽。其点马海西也。先是点官未尝入岛。府君不惮险远。遍入诸岛。风波颇顺。即欲发归。则篙工托故不欲行曰。且待明日未为晚。府君曰。此风明日连吹未可必。风逆则汝当受刑。篙工始发船。翌日逆风果作。十馀日不止。同时诸船落后留连者。粮乏仅得活。有役卒病死。命载还其尸。舟人以为不利于舟行而不肯。府君命载于自乘船。则舟人不得已载运。是时舟人咸称府君为神明。诸岛人年久后。犹称李点马云。入白翎岛时。篙工请曰。今日是崔得介溺死日。海俗以为忌。舟船不行。且致祈禳。否必致灾怪不宁。府君作小辞投海发船。是日风顺浪平。舟中无一人晕疾。为北评事也。主将张甚。奴视文士。及见府君。敬重悦服。时有筑城之役。一日雪夜。念曳石戍卒辛苦。谋得酒壶。亲往饷之。戍卒感动。主将喜甚。每曰。评事后日当为都元帅矣。
端夏入北幕时。有八十老妓聪识异常。能说府君时事曰。当时府中共称为大人。府君时年三十三矣。其为遐俗所称道如此。其时镜城判官曹公友仁别府君诗曰。非无去国泪。不敢向君垂。北人至今传诵。不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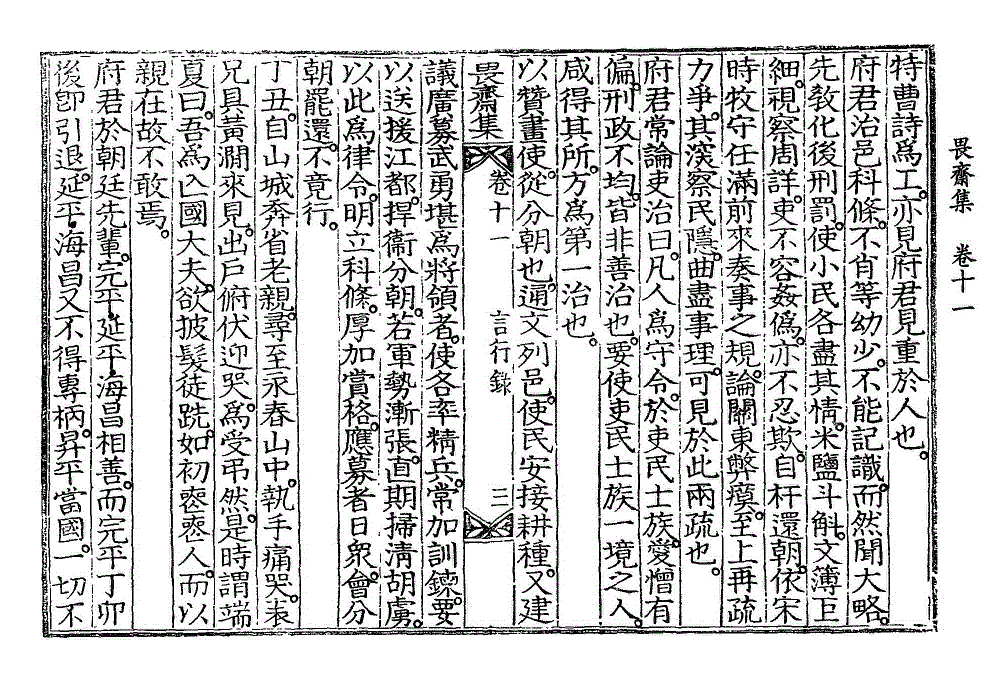 特曹诗为工。亦见府君见重于人也。
特曹诗为工。亦见府君见重于人也。府君治邑科条。不肖等幼少。不能记识。而然闻大略。先教化后刑罚。使小民各尽其情。米盐斗斛。文簿巨细。视察周详。吏不容奸伪。亦不忍欺。自杆还朝。依宋时牧守任满前来奏事之规。论关东弊瘼。至上再疏力争。其深察民隐。曲尽事理。可见于此两疏也。
府君常论吏治曰。凡人为守令。于吏民士族。爱憎有偏。刑政不均。皆非善治也。要使吏民士族一境之人。咸得其所。方为第一治也。
以赞画使。从分朝也。通文列邑。使民安接耕种。又建议广募武勇堪为将领者。使各率精兵。常加训鍊。要以送援江都。捍卫分朝。若军势渐张。直期扫清胡虏。以此为律令。明立科条。厚加赏格。应募者日众。会分朝罢还。不竟行。
丁丑。自山城奔省老亲。寻至永春山中。执手痛哭。表兄具黄涧来见。出户俯伏迎哭。为受吊然。是时谓端夏曰。吾为亡国大夫。欲披发徒跣。如初丧丧人。而以亲在故不敢焉。
府君于朝廷先辈。完平,延平,海昌相善。而完平丁卯后即引退。延平,海昌又不得专柄。升平当国。一切不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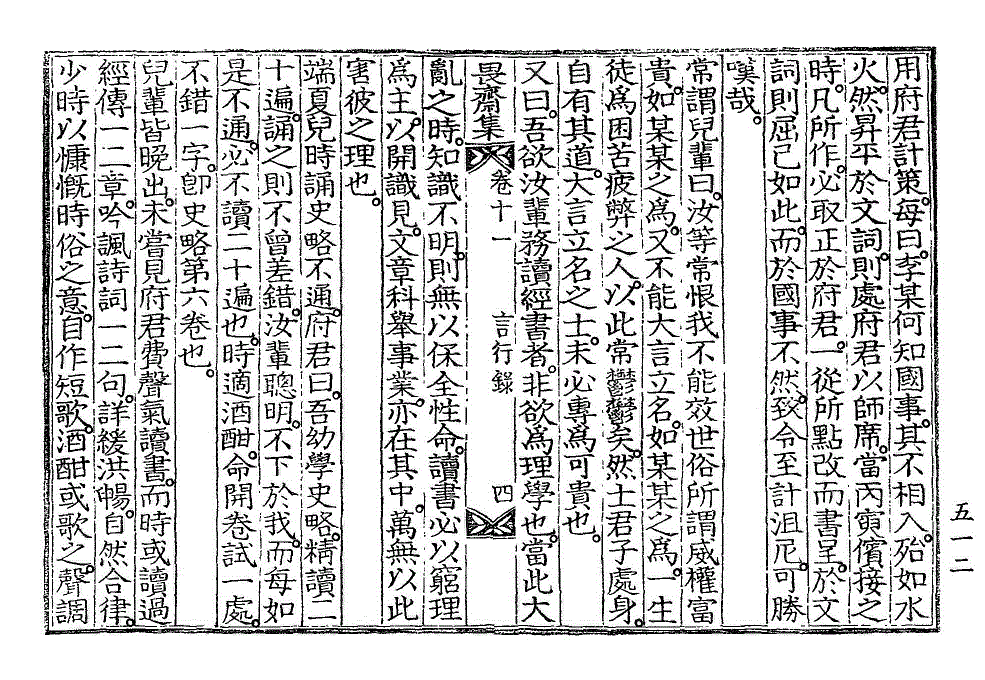 用府君计策。每曰。李某何知国事。其不相入。殆如水火。然升平于文词。则处府君以师席。当丙寅傧接之时。凡所作。必取正于府君。一从所点改而书呈。于文词则屈己如此。而于国事不然。致令至计沮尼。可胜叹哉。
用府君计策。每曰。李某何知国事。其不相入。殆如水火。然升平于文词。则处府君以师席。当丙寅傧接之时。凡所作。必取正于府君。一从所点改而书呈。于文词则屈己如此。而于国事不然。致令至计沮尼。可胜叹哉。常谓儿辈曰。汝等常恨我不能效世俗所谓威权富贵。如某某之为。又不能大言立名。如某某之为。一生徒为困苦疲弊之人。以此常郁郁矣。然士君子处身。自有其道。大言立名之士。未必专为可贵也。
又曰。吾欲汝辈务读经书者。非欲为理学也。当此大乱之时。知识不明。则无以保全性命。读书必以穷理为主。以开识见。文章科举事业。亦在其中。万无以此害彼之理也。
端夏儿时诵史略不通。府君曰。吾幼学史略。精读二十遍。诵之则不曾差错。汝辈聪明。不下于我。而每如是不通。必不读二十遍也。时适酒酣。命开卷试一处。不错一字。即史略第六卷也。
儿辈皆晚出。未尝见府君费声气读书。而时或读过经传一二章。吟讽诗词一二句。详缓洪畅。自然合律。少时以慷慨时俗之意。自作短歌。酒酣或歌之。声调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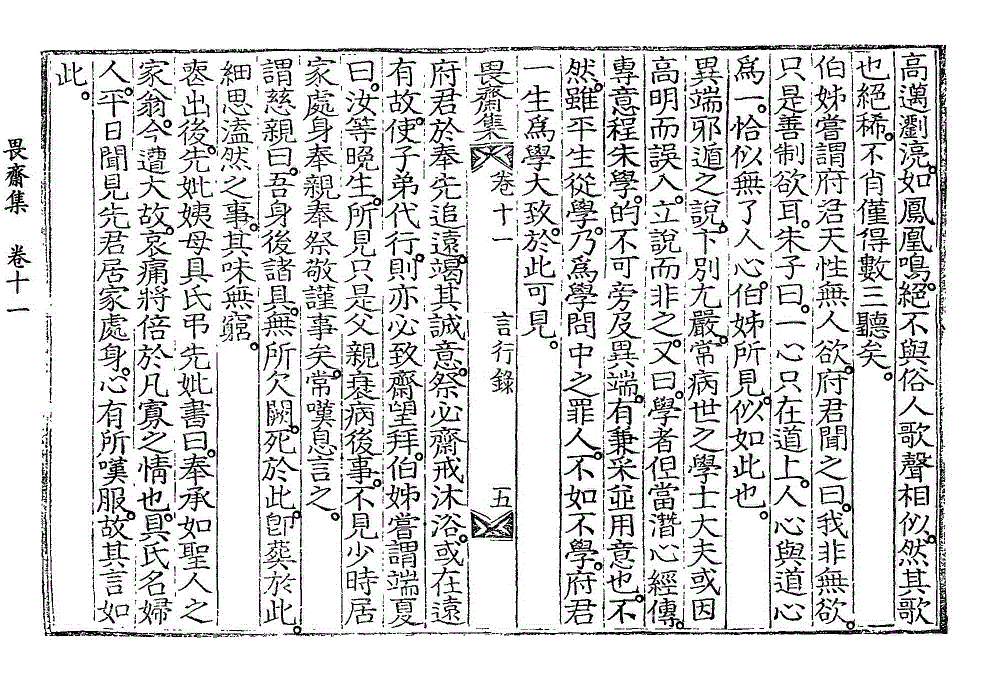 高迈浏湸。如凤凰鸣。绝不与俗人歌声相似。然其歌也绝稀。不肖仅得数三听矣。
高迈浏湸。如凤凰鸣。绝不与俗人歌声相似。然其歌也绝稀。不肖仅得数三听矣。伯姊尝谓府君天性无人欲。府君闻之曰。我非无欲。只是善制欲耳。朱子曰。一心只在道上。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人心。伯姊所见。似如此也。
异端邪遁之说。卞别尤严。常病世之学士大夫或因高明而误入。立说而非之。又曰。学者但当潜心经传。专意程朱学。的不可旁及异端。有兼采并用意也。不然。虽平生从学。乃为学问中之罪人。不如不学。府君一生为学大致。于此可见。
府君于奉先追远。竭其诚意。祭必斋戒沐浴。或在远有故。使子弟代行。则亦必致斋望拜。伯姊尝谓端夏曰。汝等晚生。所见只是父亲衰病后事。不见少时居家处身奉亲奉祭敬谨事矣。常叹息言之。
谓慈亲曰。吾身后诸具。无所欠阙。死于此。即葬于此。细思溘然之事。其味无穷。
丧出后。先妣姨母具氏吊先妣书曰。奉承如圣人之家翁。今遭大故。哀痛将倍于凡寡之情也。具氏名妇人。平日闻见先君居家处身。心有所叹服。故其言如此。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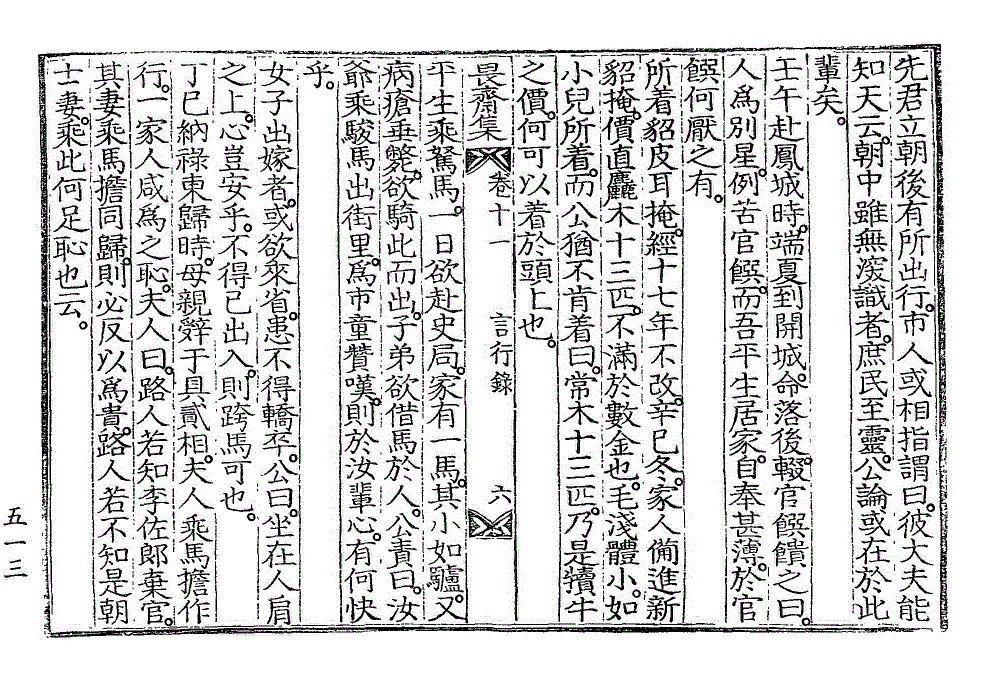 先君立朝后有所出行。市人或相指谓曰。彼大夫能知天云。朝中虽无深识者。庶民至灵。公论或在于此辈矣。
先君立朝后有所出行。市人或相指谓曰。彼大夫能知天云。朝中虽无深识者。庶民至灵。公论或在于此辈矣。壬午赴凤城时。端夏到开城。命落后。辍官馔馈之曰。人为别星。例苦官馔。而吾平生居家。自奉甚薄。于官馔何厌之有。
所着貂皮耳掩。经十七年不改。辛巳冬。家人备进新貂掩。价直粗木十三匹。不满于数金也。毛浅体小。如小儿所着。而公犹不肯着曰。常木十三匹。乃是犊牛之价。何可以着于头上也。
平生乘驽马。一日欲赴史局。家有一马。其小如驴。又病疮垂毙。欲骑此而出。子弟欲借马于人。公责曰。汝爷乘骏马出街里。为市童赞叹。则于汝辈心。有何快乎。
女子出嫁者。或欲来省。患不得轿卒。公曰。坐在人肩之上。心岂安乎。不得已出入。则跨马可也。
丁巳纳禄东归时。母亲辞于具贰相。夫人乘马担作行。一家人咸为之耻。夫人曰。路人若知李佐郎弃官。其妻乘马担同归。则必反以为贵。路人若不知是朝士妻。乘此何足耻也云。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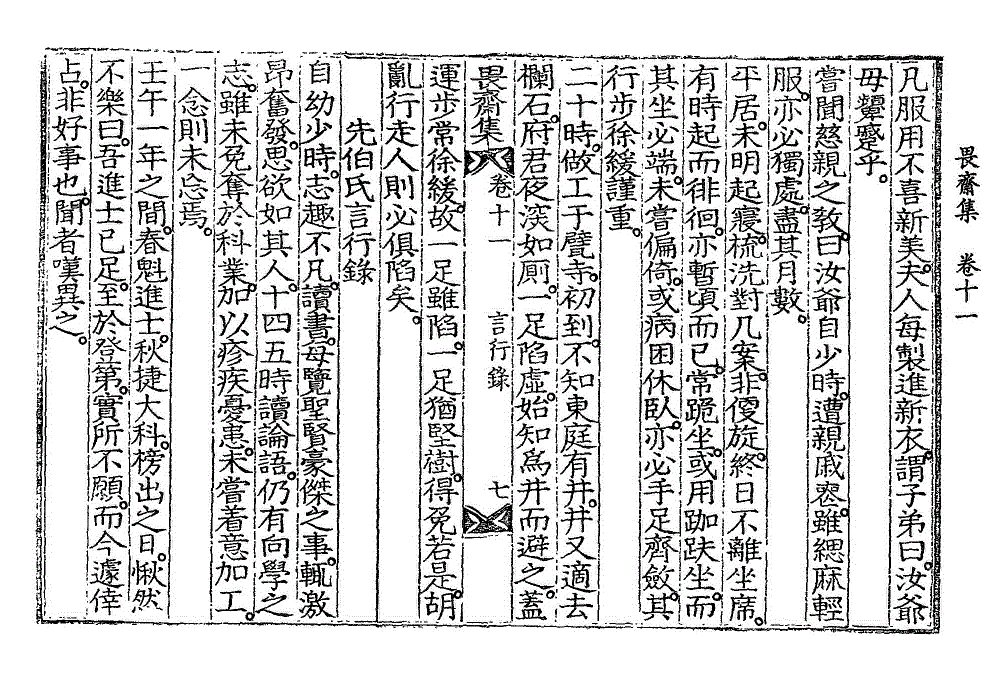 凡服用不喜新美。夫人每制进新衣。谓子弟曰。汝爷毋颦蹙乎。
凡服用不喜新美。夫人每制进新衣。谓子弟曰。汝爷毋颦蹙乎。尝闻慈亲之教。曰汝爷自少时。遭亲戚丧。虽缌麻轻服。亦必独处。尽其月数。
平居。未明起寝。梳洗对几案。非便旋。终日不离坐席。有时起而徘徊。亦暂顷而已。常跪坐。或用跏趺坐。而其坐必端。未尝偏倚。或病困休卧。亦必手足齐敛。其行步徐缓谨重。
二十时。做工于甓寺。初到。不知东庭有井。井又适去栏石。府君夜深如厕。一足陷虚。始知为井而避之。盖运步常徐缓。故一足虽陷。一足犹坚树。得免若是。胡乱行走人则必俱陷矣。
先伯氏言行录
自幼少时。志趣不凡。读书。每览圣贤豪杰之事。辄激昂奋发。思欲如其人。十四五时读论语。仍有向学之志。虽未免夺于科业。加以疹疾忧患。未尝着意加工。一念则未忘焉。
壬午一年之间。春魁进士。秋捷大科。榜出之日。愀然不乐曰。吾进士已足。至于登第。实所不愿。而今遽倖占。非好事也。闻者叹异之。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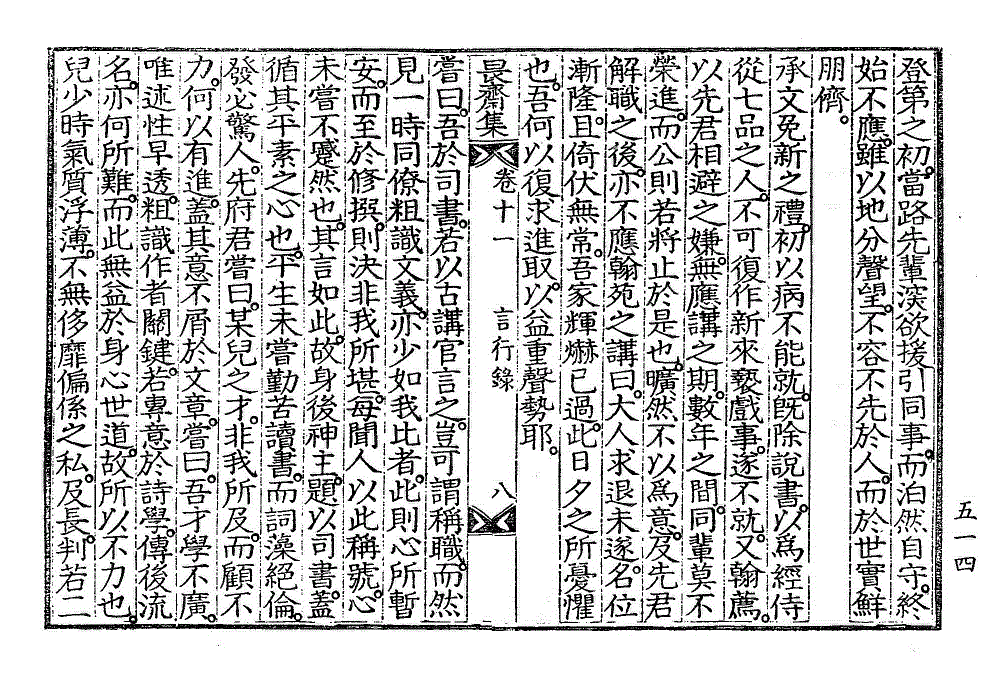 登第之初。当路先辈深欲援引同事。而泊然自守。终始不应。虽以地分声望。不容不先于人。而于世实鲜朋侪。
登第之初。当路先辈深欲援引同事。而泊然自守。终始不应。虽以地分声望。不容不先于人。而于世实鲜朋侪。承文免新之礼。初以病不能就。既除说书。以为经侍从七品之人。不可复作新来亵戏事。遂不就。又翰荐。以先君相避之嫌。无应讲之期。数年之间。同辈莫不荣进。而公则若将止于是也。旷然不以为意。及先君解职之后。亦不应翰苑之讲曰。大人求退未遂。名位渐隆。且倚伏无常。吾家辉赫已过。此日夕之所忧惧也。吾何以复求进取。以益重声势耶。
尝曰。吾于司书。若以古讲官言之。岂可谓称职。而然见一时同僚粗识文义。亦少如我比者。此则心所暂安。而至于修撰。则决非我所堪。每闻人以此称号。心未尝不蹙然也。其言如此。故身后神主。题以司书。盖循其平素之心也。平生未尝勤苦读书。而词藻绝伦。发必惊人。先府君尝曰。某儿之才。非我所及。而顾不力。何以有进。盖其意不屑于文章。尝曰。吾才学不广。唯述性早透。粗识作者关键。若专意于诗学。传后流名。亦何所难。而此无益于身心世道。故所以不力也。儿少时气质浮薄。不无侈靡偏系之私。及长。判若二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5H 页
 人。其视名利浮荣。不啻若浼。居常处心廓然公平。发言作事。无一毫矫伪。皆出于至诚恻怛。若天性然。虽家庭训教。自然化成。而然非向学之心禀才之美。何能变化之若是乎。
人。其视名利浮荣。不啻若浼。居常处心廓然公平。发言作事。无一毫矫伪。皆出于至诚恻怛。若天性然。虽家庭训教。自然化成。而然非向学之心禀才之美。何能变化之若是乎。及遭大故后。思过于无过之地。痛悔平生未尽之事。日夜刻厉。惧或失坠先训。非徒自勉。亦以诲谕两弟。如恐不及。其操心行事。视平日。又不啻别人矣。
先府君遗戒贬葬。至不用石灰。一家亲丈有以书来言其难于奉行。答书略曰。石灰一事。非出于一时偶然遗戒。乃自丁丑草土病重之时。已有此命载诸文字。厥后十馀年间。寻常言说。至于今番。又加丁宁。其意盖以罪人自贬。而复古礼从先进之意。亦未必不寓于其间。决非寻常世俗知见之所能到。况以不肖无状。岂敢一毫违越。又谕一家诸人曰。先君遗戒之事。皆出于义理之至当。非故为崖异之行也。为人子者。虽乱命。亦难轻违。况至当治命。何敢不遵乎。其当大事处变礼。务尽诚孝如此。处攀擗澌毁之中。而昼则监董山役。夜则讲求葬礼。至于一礼节之微。一凡具之细。亦必精勤亲审。不委他人。其于毋使土亲肤之道。亦代以他制。竟底于无憾而后已。祇奉几筵。一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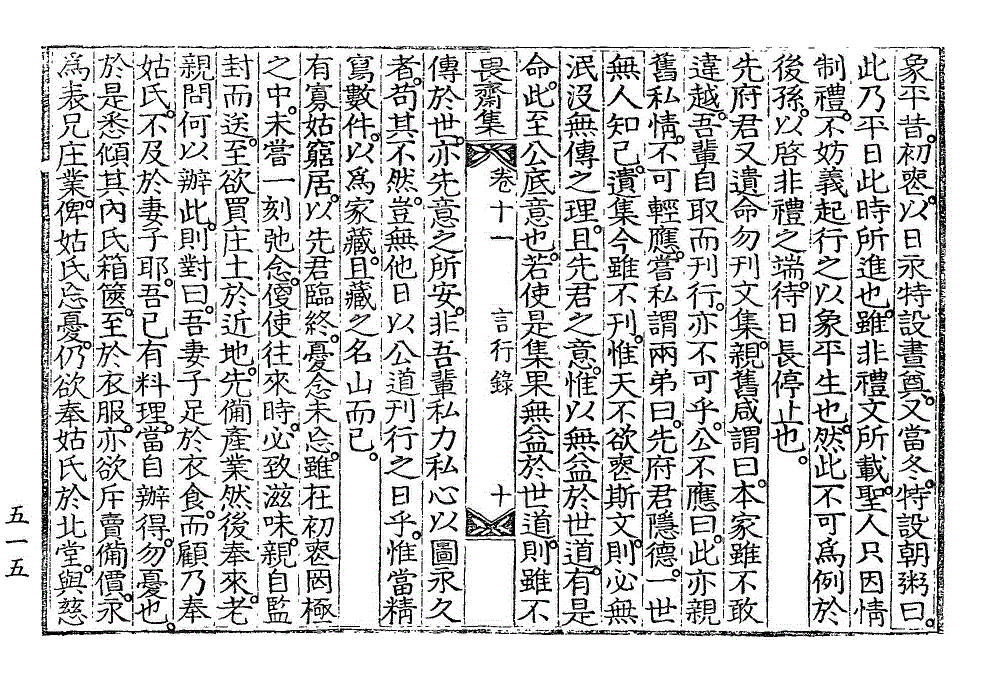 象平昔。初丧。以日永特设昼奠。又当冬。特设朝粥曰。此乃平日此时所进也。虽非礼文所载。圣人只因情制礼。不妨义起行之以象平生也。然此不可为例于后孙。以启非礼之端。待日长停止也。
象平昔。初丧。以日永特设昼奠。又当冬。特设朝粥曰。此乃平日此时所进也。虽非礼文所载。圣人只因情制礼。不妨义起行之以象平生也。然此不可为例于后孙。以启非礼之端。待日长停止也。先府君又遗命勿刊文集。亲旧咸谓曰。本家虽不敢违越。吾辈自取而刊行。亦不可乎。公不应曰。此亦亲旧私情。不可轻应。尝私谓两弟曰。先府君隐德。一世无人知已。遗集今虽不刊。惟天不欲丧斯文。则必无泯没无传之理。且先君之意。惟以无益于世道。有是命。此至公底意也。若使是集果无益于世道。则虽不传于世。亦先意之所安。非吾辈私力私心以图永久者。苟其不然。岂无他日以公道刊行之日乎。惟当精写数件。以为家藏。且藏之名山而已。
有寡姑穷居。以先君临终。忧念未忘。虽在初丧罔极之中。未尝一刻弛念。便使往来时。必致滋味。亲自监封而送。至欲买庄土于近地。先备产业然后奉来。老亲问何以办此。则对曰。吾妻子足于衣食。而顾乃奉姑氏。不及于妻子耶。吾已有料理。当自办得。勿忧也。于是悉倾其内氏箱箧。至于衣服。亦欲斥卖备价。永为表兄庄业。俾姑氏忘忧。仍欲奉姑氏于北堂。与慈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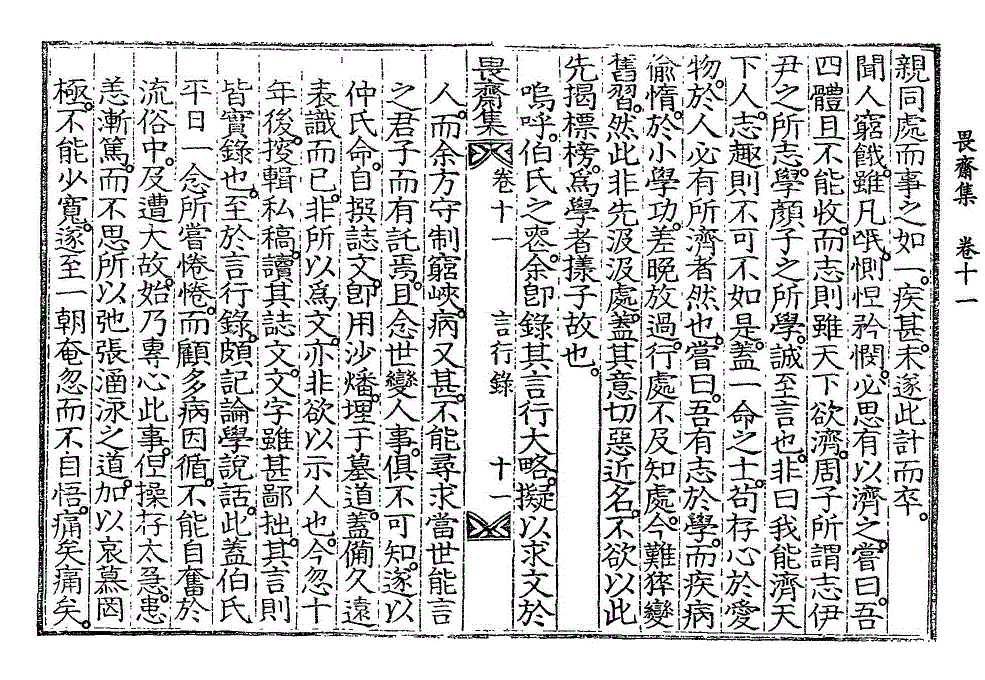 亲同处而事之如一。疾甚。未遂此计而卒。
亲同处而事之如一。疾甚。未遂此计而卒。闻人穷饿。虽凡氓。恻怛矜悯。必思有以济之。尝曰。吾四体且不能收。而志则虽天下欲济。周子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诚至言也。非曰我能济天下人。志趣则不可不如是。盖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者然也。尝曰。吾有志于学。而疾病偷惰。于小学功。差晚放过。行处不及知处。今难猝变旧习。然此非先汲汲处。盖其意切恶近名。不欲以此先揭标榜。为学者样子故也。
呜呼。伯氏之丧。余即录其言行大略。拟以求文于人。而余方守制穷峡。病又甚。不能寻求当世能言之君子而有托焉。且念世变人事。俱不可知。遂以仲氏命。自撰志文。即用沙燔。埋于墓道。盖备久远表识而已。非所以为文。亦非欲以示人也。今忽十年后。搜辑私稿。读其志文。文字虽甚鄙拙。其言则皆实录也。至于言行录。颇记论学说话。此盖伯氏平日一念所尝惓惓。而顾多病因循。不能自奋于流俗中。及遭大故。始乃专心此事。但操存太急。患恙渐笃。而不思所以弛张涵泳之道。加以哀慕罔极。不能少宽。遂至一朝奄忽而不自悟。痛矣痛矣。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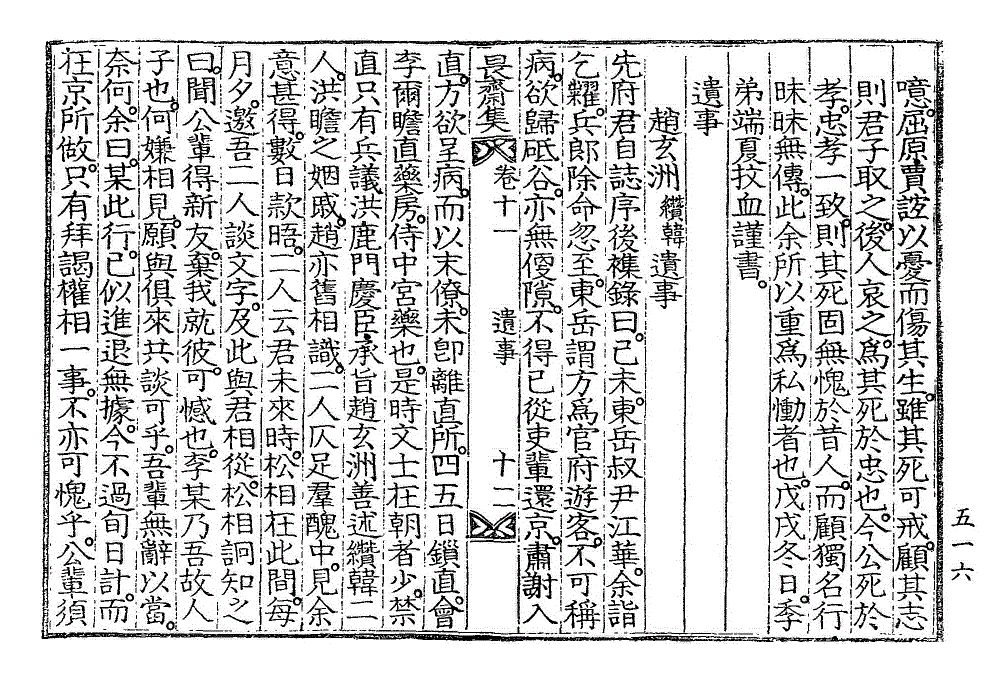 噫。屈原,贾谊以忧而伤其生。虽其死可戒。顾其志则君子取之。后人哀之。为其死于忠也。今公死于孝。忠孝一致。则其死固无愧于昔人。而顾独名行昧昧无传。此余所以重为私恸者也。戊戌冬日。季弟端夏抆血谨书。
噫。屈原,贾谊以忧而伤其生。虽其死可戒。顾其志则君子取之。后人哀之。为其死于忠也。今公死于孝。忠孝一致。则其死固无愧于昔人。而顾独名行昧昧无传。此余所以重为私恸者也。戊戌冬日。季弟端夏抆血谨书。畏斋集卷之十一
遗事
赵玄洲(缵韩)遗事
先府君自志序后杂录曰。己未。东岳叔尹江华。余诣乞粜。兵郎除命忽至。东岳谓方为官府游客。不可称病。欲归砥谷。亦无便隙。不得已从吏辈还京。肃谢入直。方欲呈病。而以末僚。未即离直所。四五日锁直。会李尔瞻直药房。侍中宫药也。是时文士在朝者少。禁直只有兵议洪鹿门庆臣,承旨赵玄洲善述缵韩二人。洪瞻之姻戚。赵亦旧相识。二人仄足群丑中。见余意甚得。数日款晤。二人云君未来时。松相在此间。每月夕。邀吾二人谈文字。及此与君相从。松相诇知之曰。闻公辈得新友。弃我就彼。可憾也。李某乃吾故人子也。何嫌相见。愿与俱来共谈可乎。吾辈无辞以当。奈何。余曰。某此行。已似进退无据。今不过旬日讣。而在京所做。只有拜谒权相一事。不亦可愧乎。公辈须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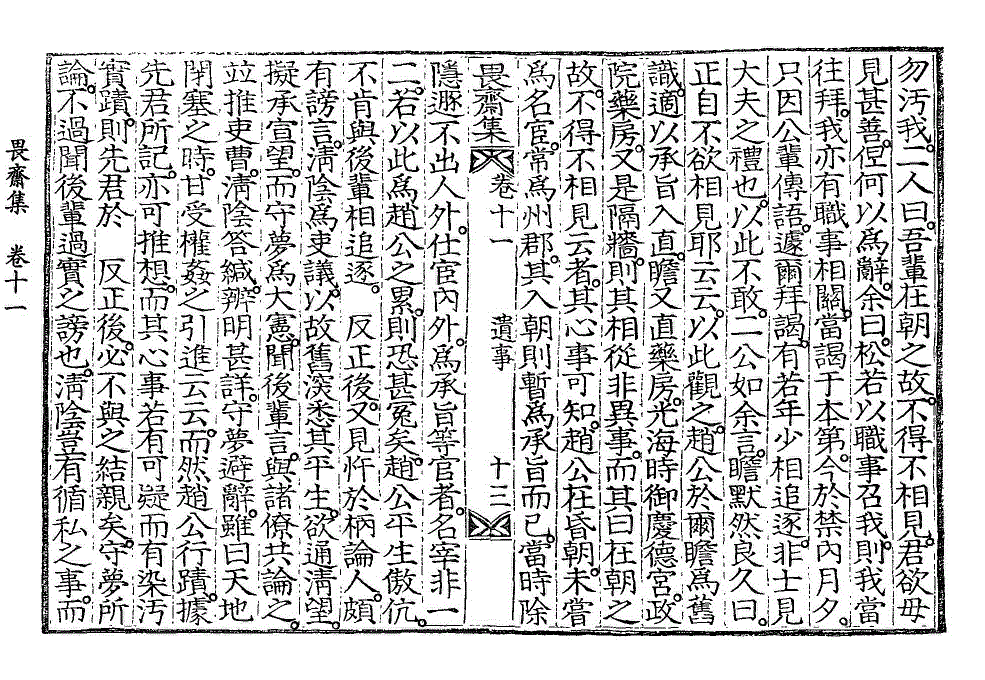 勿污我。二人曰。吾辈在朝之故。不得不相见。君欲毋见甚善。但何以为辞。余曰。松若以职事召我。则我当往拜。我亦有职事相关。当谒于本第。今于禁内月夕。只因公辈传语。遽尔拜谒。有若年少相追逐。非士见大夫之礼也。以此不敢。二公如余言。瞻默然良久曰。正自不欲相见耶云云。以此观之。赵公于尔瞻为旧识。适以承旨入直。瞻又直药房。光海时御庆德宫。政院药房。又是隔墙。则其相从非异事。而其曰在朝之故。不得不相见云者。其心事可知。赵公在昏朝。未尝为名宦。常为州郡。其入朝则暂为承旨而已。当时除隐遁不出人外。仕宦内外。为承旨等官者。名宰非一二。若以此为赵公之累。则恐甚冤矣。赵公平生傲伉。不肯与后辈相追逐。 反正后。又见忤于柄论人。颇有谤言。清阴为吏议。以故旧深悉其平生。欲通清望。拟承宣望。而守梦为大宪。闻后辈言。与诸僚共论之。并推吏曹。清阴答缄。辨明甚详。守梦避辞。虽曰天地闭塞之时。甘受权奸之引进云云。而然赵公行迹。据先君所记。亦可推想。而其心事若有可疑而有染污实迹。则先君于 反正后。必不与之结亲矣。守梦所论。不过闻后辈过实之谤也。清阴岂有循私之事。而
勿污我。二人曰。吾辈在朝之故。不得不相见。君欲毋见甚善。但何以为辞。余曰。松若以职事召我。则我当往拜。我亦有职事相关。当谒于本第。今于禁内月夕。只因公辈传语。遽尔拜谒。有若年少相追逐。非士见大夫之礼也。以此不敢。二公如余言。瞻默然良久曰。正自不欲相见耶云云。以此观之。赵公于尔瞻为旧识。适以承旨入直。瞻又直药房。光海时御庆德宫。政院药房。又是隔墙。则其相从非异事。而其曰在朝之故。不得不相见云者。其心事可知。赵公在昏朝。未尝为名宦。常为州郡。其入朝则暂为承旨而已。当时除隐遁不出人外。仕宦内外。为承旨等官者。名宰非一二。若以此为赵公之累。则恐甚冤矣。赵公平生傲伉。不肯与后辈相追逐。 反正后。又见忤于柄论人。颇有谤言。清阴为吏议。以故旧深悉其平生。欲通清望。拟承宣望。而守梦为大宪。闻后辈言。与诸僚共论之。并推吏曹。清阴答缄。辨明甚详。守梦避辞。虽曰天地闭塞之时。甘受权奸之引进云云。而然赵公行迹。据先君所记。亦可推想。而其心事若有可疑而有染污实迹。则先君于 反正后。必不与之结亲矣。守梦所论。不过闻后辈过实之谤也。清阴岂有循私之事。而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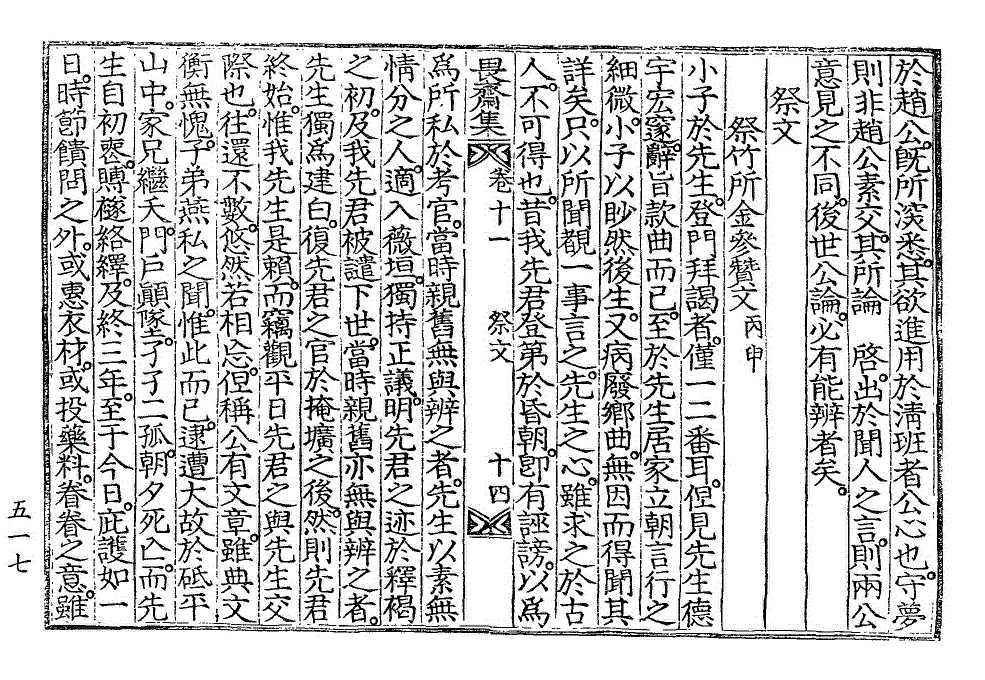 于赵公。既所深悉。其欲进用于清班者公心也。守梦则非赵公素交。其所论 启。出于闻人之言。则两公意见之不同。后世公论。必有能辨者矣。
于赵公。既所深悉。其欲进用于清班者公心也。守梦则非赵公素交。其所论 启。出于闻人之言。则两公意见之不同。后世公论。必有能辨者矣。畏斋集卷之十一
祭文
祭竹所金参赞文(丙申)
小子于先生。登门拜谒者。仅一二番耳。但见先生德宇宏邃。辞旨款曲而已。至于先生居家立朝言行之细微。小子以眇然后生。又病废乡曲。无因而得闻其详矣。只以所闻睹一事言之。先生之心。虽求之于古人。不可得也。昔我先君登第于昏朝。即有诬谤。以为为所私于考官。当时亲旧无与辨之者。先生以素无情分之人。适入薇垣。独持正议。明先君之迹于释褐之初。及我先君被谴下世。当时亲旧亦无与辨之者。先生独为建白。复先君之官于掩圹之后。然则先君终始。惟我先生是赖。而窃观平日先君之与先生交际也。往还不数。悠然若相忘。但称公有文章。虽典文衡无愧。子弟燕私之闻。惟此而已。逮遭大故于砥平山中。家兄继夭。门户颠坠。孑孑二孤。朝夕死亡。而先生自初丧。赙襚络绎。及终三年。至于今日。庇护如一日。时节馈问之外。或惠衣材。或投药料。眷眷之意。虽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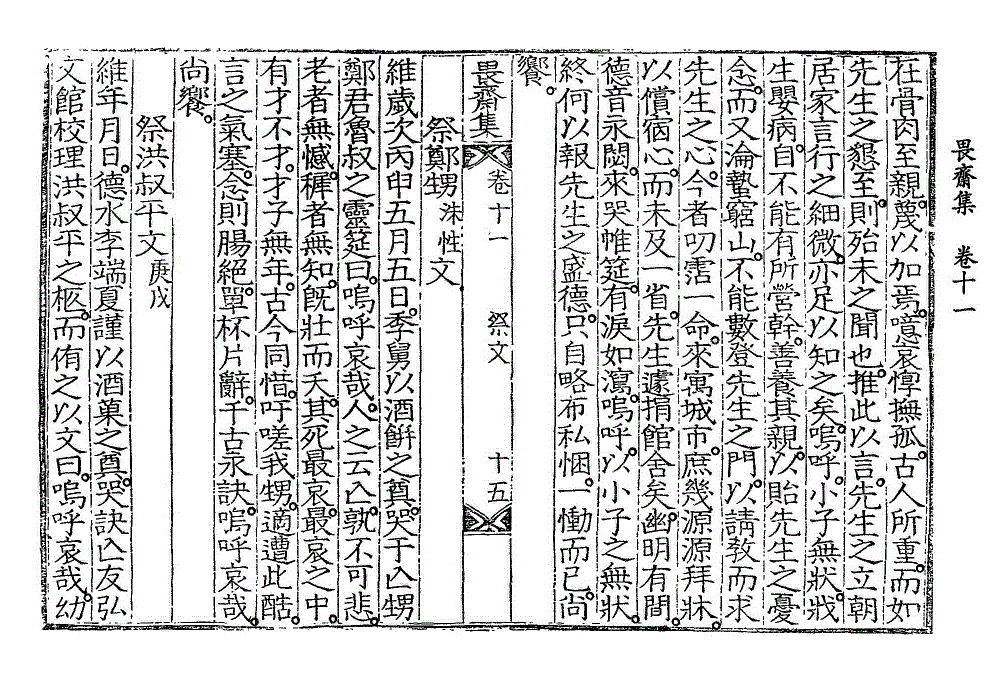 在骨肉至亲。蔑以加焉。噫哀茕抚孤。古人所重。而如先生之恳至。则殆未之闻也。推此以言。先生之立朝居家言行之细微。亦足以知之矣。呜呼。小子无状。戕生婴病。自不能有所营干。善养其亲。以贻先生之忧念。而又沦蛰穷山。不能数登先生之门。以请教而求先生之心。今者叨沾一命。来寓城市。庶几源源拜床。以偿宿心。而未及省。先生遽捐馆舍矣。幽明有间。德音永閟。来哭帷筵。有泪如泻。呜呼。以小子之无状。终何以报先生之盛德。只自略布私悃。一恸而已。尚飨。
在骨肉至亲。蔑以加焉。噫哀茕抚孤。古人所重。而如先生之恳至。则殆未之闻也。推此以言。先生之立朝居家言行之细微。亦足以知之矣。呜呼。小子无状。戕生婴病。自不能有所营干。善养其亲。以贻先生之忧念。而又沦蛰穷山。不能数登先生之门。以请教而求先生之心。今者叨沾一命。来寓城市。庶几源源拜床。以偿宿心。而未及省。先生遽捐馆舍矣。幽明有间。德音永閟。来哭帷筵。有泪如泻。呜呼。以小子之无状。终何以报先生之盛德。只自略布私悃。一恸而已。尚飨。祭郑甥(洙性)文
维岁次丙申五月五日。季舅以酒饼之奠。哭于亡甥郑君鲁叔之灵筵曰。呜呼哀哉。人之云亡。孰不可悲。老者无憾。稚者无知。既壮而夭。其死最哀。最哀之中。有才不才。才子无年。古今同惜。吁嗟我甥。适遭此酷。言之气塞。念则肠绝。单杯片辞。千古永诀。呜呼哀哉。尚飨。
祭洪叔平文(庚戌)
维年月日。德水李端夏谨以酒果之奠。哭诀亡友弘文馆校理洪叔平之柩。而侑之以文曰。呜呼哀哉。幼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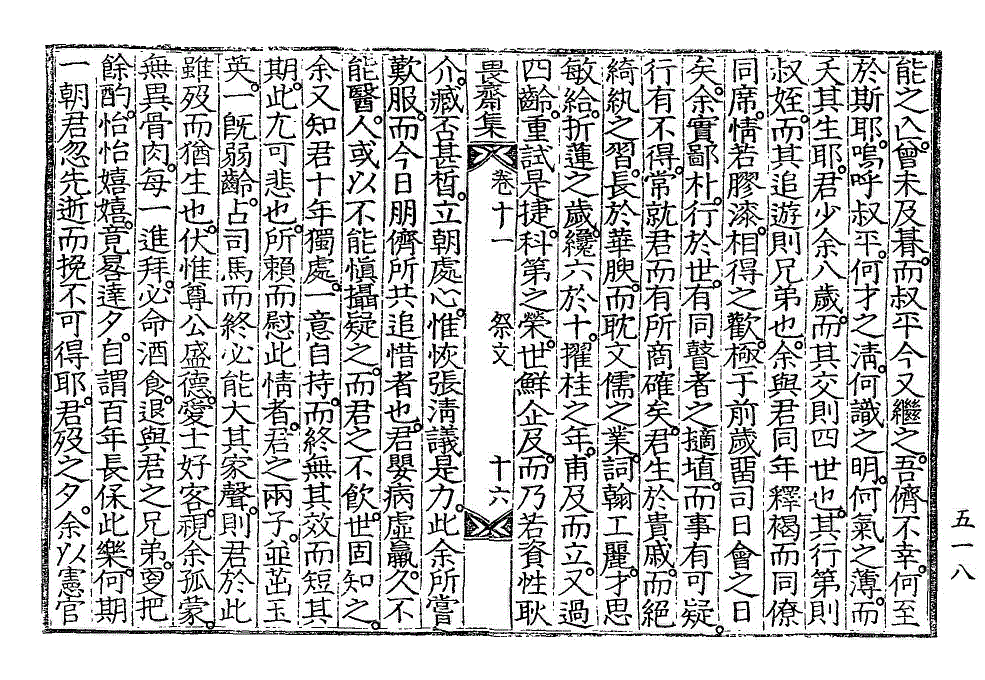 能之亡。曾未及期。而叔平今又继之。吾侪不幸。何至于斯耶。呜呼叔平。何才之清。何识之明。何气之薄。而夭其生耶。君少余八岁。而其交则四世也。其行第则叔侄。而其追游则兄弟也。余与君同年释褐而同僚同席。情若胶漆。相得之欢。极于前岁留司日会之日矣。余实鄙朴。行于世。有同瞽者之擿埴。而事有可疑。行有不得。常就君而有所商确矣。君生于贵戚。而绝绮纨之习。长于华腴。而耽文儒之业。词翰工丽。才思敏给。折莲之岁。才六于十。擢桂之年。甫及而立。又过四龄。重试是捷。科第之荣。世鲜企及。而乃若资性耿介。臧否甚晰。立朝处心。惟恢张清议是力。此余所尝叹服。而今日朋侪所共追惜者也。君婴病虚羸。久不能医。人或以不能慎摄疑之。而君之不饮。世固知之。余又知君十年独处。一意自持。而终无其效而短其期。此尤可悲也。所赖而慰此情者。君之两子。并茁玉英。一既弱龄。占司马而终必能大其家声。则君于此虽殁而犹生也。伏惟尊公盛德。爱士好客。视余孤蒙。无异骨肉。每一进拜。必命酒食。退与君之兄弟。更把馀酌。怡怡嬉嬉。竟晷达夕。自谓百年长保此乐。何期一朝君忽先逝而挽不可得耶。君殁之夕。余以宪官
能之亡。曾未及期。而叔平今又继之。吾侪不幸。何至于斯耶。呜呼叔平。何才之清。何识之明。何气之薄。而夭其生耶。君少余八岁。而其交则四世也。其行第则叔侄。而其追游则兄弟也。余与君同年释褐而同僚同席。情若胶漆。相得之欢。极于前岁留司日会之日矣。余实鄙朴。行于世。有同瞽者之擿埴。而事有可疑。行有不得。常就君而有所商确矣。君生于贵戚。而绝绮纨之习。长于华腴。而耽文儒之业。词翰工丽。才思敏给。折莲之岁。才六于十。擢桂之年。甫及而立。又过四龄。重试是捷。科第之荣。世鲜企及。而乃若资性耿介。臧否甚晰。立朝处心。惟恢张清议是力。此余所尝叹服。而今日朋侪所共追惜者也。君婴病虚羸。久不能医。人或以不能慎摄疑之。而君之不饮。世固知之。余又知君十年独处。一意自持。而终无其效而短其期。此尤可悲也。所赖而慰此情者。君之两子。并茁玉英。一既弱龄。占司马而终必能大其家声。则君于此虽殁而犹生也。伏惟尊公盛德。爱士好客。视余孤蒙。无异骨肉。每一进拜。必命酒食。退与君之兄弟。更把馀酌。怡怡嬉嬉。竟晷达夕。自谓百年长保此乐。何期一朝君忽先逝而挽不可得耶。君殁之夕。余以宪官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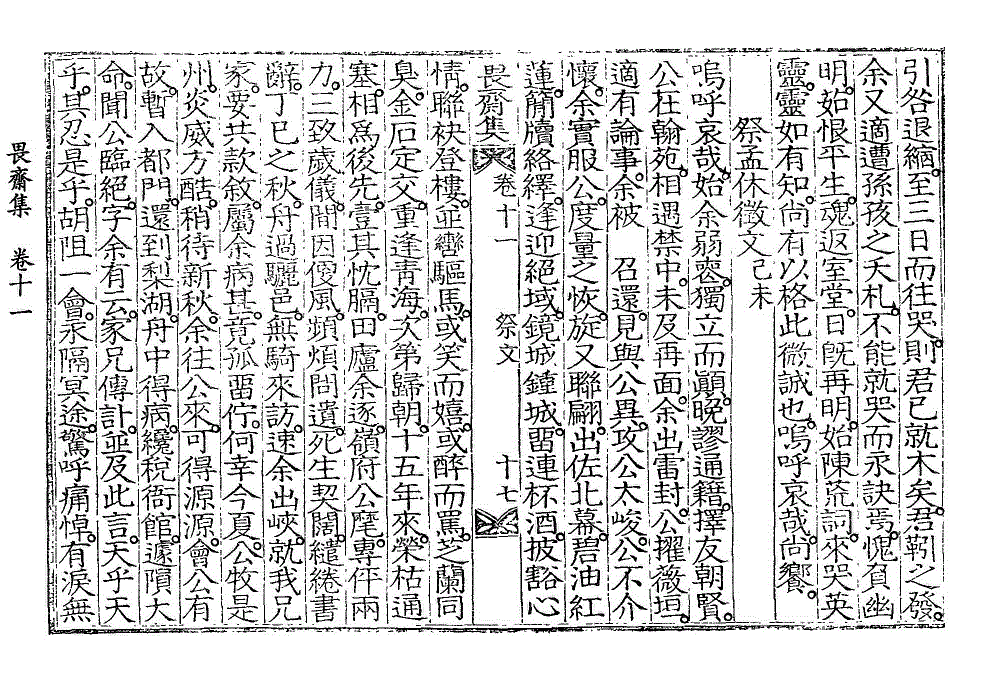 引咎退缩。至三日而往哭。则君已就木矣。君靷之发。余又适遭孙孩之夭札。不能就哭而永诀焉。愧负幽明。茹恨平生。魂返室堂。日既再明。始陈荒词。来哭英灵。灵如有知。尚有以格此微诚也。呜呼哀哉。尚飨。
引咎退缩。至三日而往哭。则君已就木矣。君靷之发。余又适遭孙孩之夭札。不能就哭而永诀焉。愧负幽明。茹恨平生。魂返室堂。日既再明。始陈荒词。来哭英灵。灵如有知。尚有以格此微诚也。呜呼哀哉。尚飨。祭孟休徵文(己未)
呜呼哀哉。始余弱丧。独立而颠。晚谬通籍。择友朝贤。公在翰苑。相遇禁中。未及再面。余出雷封。公擢薇垣。适有论事。余被 召还。见与公异。攻公太峻。公不介怀。余实服公。度量之恢。旋又联翩。出佐北幕。碧油红莲。简牍络绎。逢迎绝域。镜城钟城。留连杯酒。披豁心情。联袂登楼。并辔驱马。或笑而嬉。或醉而骂。芝兰同臭。金石定交。重逢青海。次第归朝。十五年来。荣枯通塞。相为后先。壹其忱膈。田庐余逐。岭府公麾。专伻两力。三致岁仪。间因便风。频烦问遗。死生契阔。缱绻书辞。丁巳之秋。舟过骊邑。无骑来访。速余出峡。就我兄家。要共款叙。属余病甚。竟孤留伫。何幸今夏。公牧是州。炎威方酷。稍待新秋。余往公来。可得源源。会公有故。暂入都门。还到梨湖。舟中得病。才税衙馆。遽陨大命。闻公临绝。字余有云。家兄传讣。并及此言。天乎天乎。其忍是乎。胡阻一会。永隔冥途。惊呼痛悼。有泪无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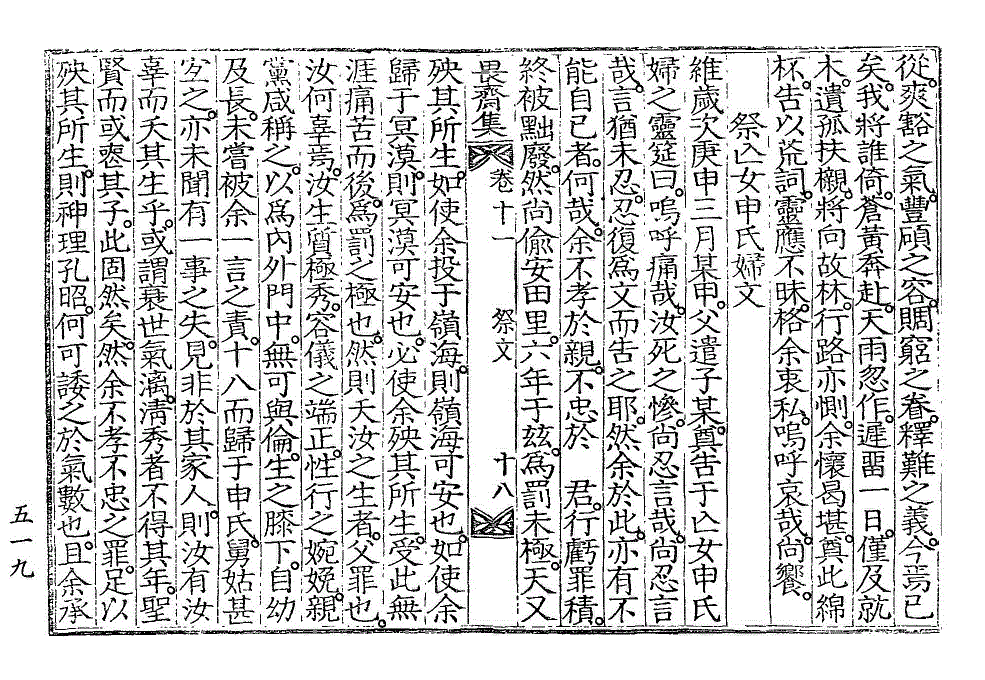 从。爽豁之气。丰硕之容。赒穷之眷。释难之义。今焉已矣。我将谁倚。苍黄奔赴。天雨忽作。迟留一日。仅及就木。遗孤扶榇。将向故林。行路亦恻。余怀曷堪。奠此绵杯。告以荒词。灵应不昧。格余衷私。呜呼哀哉。尚飨。
从。爽豁之气。丰硕之容。赒穷之眷。释难之义。今焉已矣。我将谁倚。苍黄奔赴。天雨忽作。迟留一日。仅及就木。遗孤扶榇。将向故林。行路亦恻。余怀曷堪。奠此绵杯。告以荒词。灵应不昧。格余衷私。呜呼哀哉。尚飨。祭亡女申氏妇文
维岁次庚申三月某甲。父遣子某。奠告于亡女申氏妇之灵筵曰。呜呼痛哉。汝死之惨。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言犹未忍。忍复为文而告之耶。然余于此。亦有不能自已者。何哉。余不孝于亲。不忠于 君。行亏罪积。终被黜废。然尚偷安田里。六年于玆。为罚未极。天又殃其所生。如使余投于岭海。则岭海可安也。如使余归于冥漠。则冥漠可安也。必使余殃其所生。受此无涯痛苦而后。为罚之极也。然则夭汝之生者。父罪也汝何辜焉。汝生质极秀。容仪之端正。性行之婉娩。亲党咸称之。以为内外门中。无可与伦。生之膝下。自幼及长。未尝被余一言之责。十八而归于申氏。舅姑甚宜之。亦未闻有一事之失。见非于其家人。则汝有汝辜而夭其生乎。或谓衰世气漓。清秀者不得其年。圣贤而或丧其子。此固然矣。然余不孝不忠之罪。足以殃其所生。则神理孔昭。何可诿之于气数也。且余承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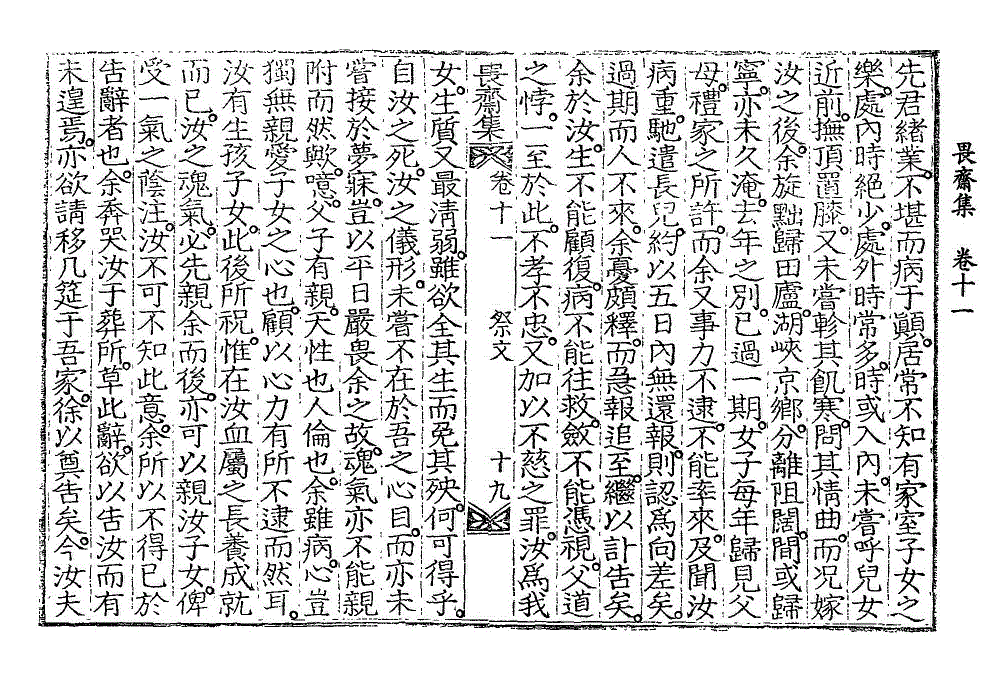 先君绪业。不堪而病于颠。居常不知有家室子女之乐。处内时绝少。处外时常多。时或入内。未尝呼儿女近前。抚顶置膝。又未尝轸其饥寒。问其情曲。而况嫁汝之后。余旋黜归田庐。湖峡京乡。分离阻阔。间或归宁。亦未久淹。去年之别。已过一期。女子每年归见父母。礼家之所许。而余又事力不逮。不能率来。及闻汝病重。驰遣长儿。约以五日内无还报。则认为向差矣。过期而人不来。余忧颇释。而急报追至。继以讣告矣。余于汝。生不能顾复。病不能往救。敛不能凭视。父道之悖。一至于此。不孝不忠。又加以不慈之罪。汝为我女。生质又最清弱。虽欲全其生而免其殃。何可得乎。自汝之死。汝之仪形。未尝不在于吾之心目。而亦未尝接于梦寐。岂以平日严畏余之故。魂气亦不能亲附而然欤。噫。父子有亲。天性也人伦也。余虽病。心岂独无亲爱子女之心也。顾以心力有所不逮而然耳。汝有生孩子女。此后所祝。惟在汝血属之长养成就而已。汝之魂气。必先亲余而后。亦可以亲汝子女。俾受一气之荫注。汝不可不知此意。余所以不得已于告辞者也。余奔哭汝于葬所。草此辞。欲以告汝而有未遑焉。亦欲请移几筵于吾家。徐以奠告矣。今汝夫
先君绪业。不堪而病于颠。居常不知有家室子女之乐。处内时绝少。处外时常多。时或入内。未尝呼儿女近前。抚顶置膝。又未尝轸其饥寒。问其情曲。而况嫁汝之后。余旋黜归田庐。湖峡京乡。分离阻阔。间或归宁。亦未久淹。去年之别。已过一期。女子每年归见父母。礼家之所许。而余又事力不逮。不能率来。及闻汝病重。驰遣长儿。约以五日内无还报。则认为向差矣。过期而人不来。余忧颇释。而急报追至。继以讣告矣。余于汝。生不能顾复。病不能往救。敛不能凭视。父道之悖。一至于此。不孝不忠。又加以不慈之罪。汝为我女。生质又最清弱。虽欲全其生而免其殃。何可得乎。自汝之死。汝之仪形。未尝不在于吾之心目。而亦未尝接于梦寐。岂以平日严畏余之故。魂气亦不能亲附而然欤。噫。父子有亲。天性也人伦也。余虽病。心岂独无亲爱子女之心也。顾以心力有所不逮而然耳。汝有生孩子女。此后所祝。惟在汝血属之长养成就而已。汝之魂气。必先亲余而后。亦可以亲汝子女。俾受一气之荫注。汝不可不知此意。余所以不得已于告辞者也。余奔哭汝于葬所。草此辞。欲以告汝而有未遑焉。亦欲请移几筵于吾家。徐以奠告矣。今汝夫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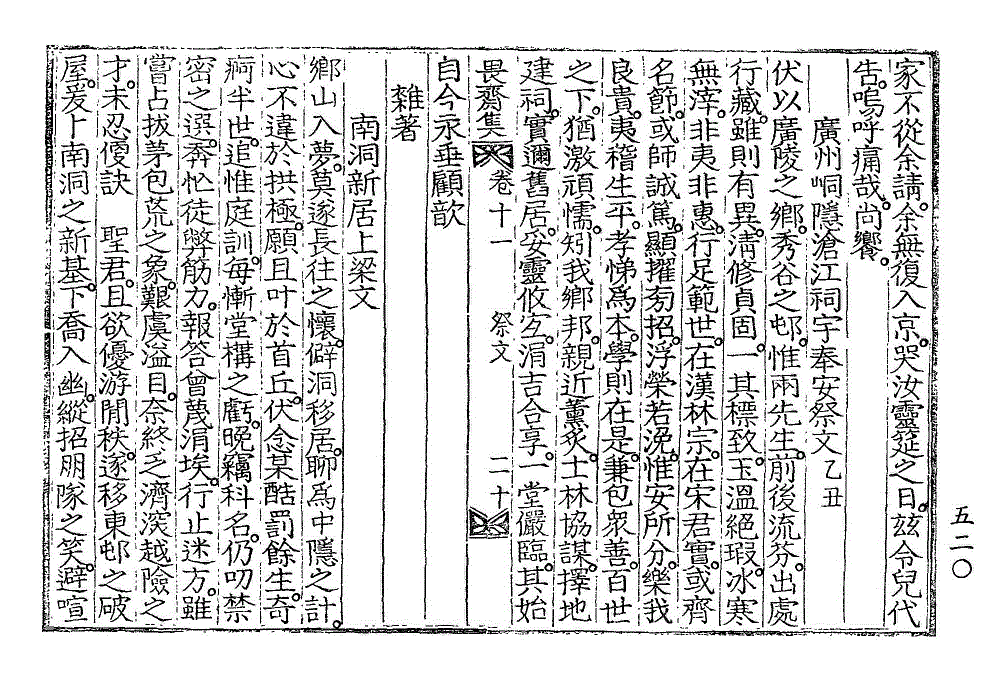 家不从余请。余无复入京。哭汝灵筵之日。玆令儿代告。呜呼痛哉。尚飨。
家不从余请。余无复入京。哭汝灵筵之日。玆令儿代告。呜呼痛哉。尚飨。广州峒隐沧江祠宇奉安祭文(乙丑)
伏以广陵之乡。秀谷之村。惟两先生。前后流芬。出处行藏。虽则有异。清修贞固。一其标致。玉温绝瑕。冰寒无滓。非夷非惠。行足范世。在汉林宗。在宋君实。或齐名节。或师诚笃。显擢旁招。浮荣若浼。惟安所分。乐我良贵。夷稽生平。孝悌为本。学则在是。兼包众善。百世之下。犹激顽懦。矧我乡邦。亲近薰炙。士林协谋。择地建祠。实迩旧居。妥灵攸宜。涓吉合享。一堂俨临。其始自今永垂顾歆
畏斋集卷之十一
杂著
南洞新居上梁文
乡山入梦。莫遂长往之怀。僻洞移居。聊为中隐之计。心不违于拱极。愿且叶于首丘。伏念某酷罚馀生。奇痾半世。追惟庭训。每惭堂构之亏。晚窃科名。仍叨禁密之选。奔忙徒弊筋力。报答曾蔑涓埃。行止迷方。虽尝占拔茅包荒之象。艰虞溢目。奈终乏济深越险之才。未忍便诀 圣君。且欲优游閒秩。遂移东村之破屋。爰卜南洞之新基。下乔入幽。纵招朋队之笑。避喧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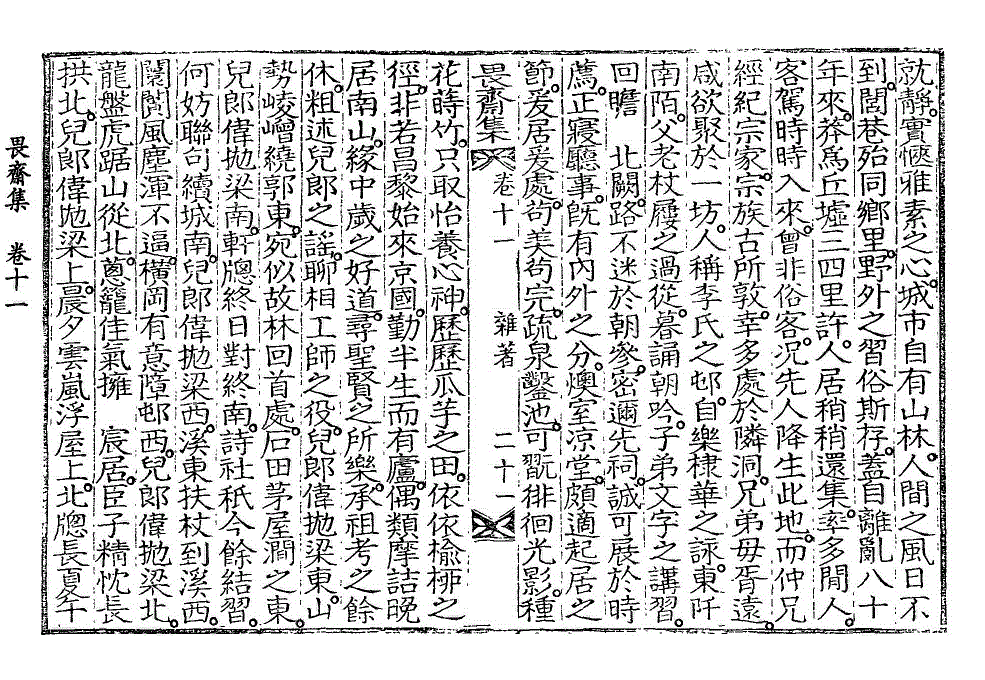 就静。实惬雅素之心。城市自有山林。人间之风日不到。闾巷殆同乡里。野外之习俗斯存。盖自离乱八十年来。莽为丘墟三四里许。人居稍稍还集。率多閒人。客驾时时入来。曾非俗客。况先人降生此地。而仲兄经纪宗家。宗族古所敦。幸多处于邻洞。兄弟毋胥远。咸欲聚于一坊。人称李氏之村。自乐棣华之咏。东阡南陌。父老杖屦之过从。暮诵朝吟。子弟文字之讲习。回瞻 北阙。路不迷于朝参。密迩先祠。诚可展于时荐。正寝厅事。既有内外之分。燠室凉堂。颇适起居之节。爰居爰处。苟美苟完。疏泉凿池。可玩徘徊光影。种花莳竹。只取怡养心神。历历瓜芋之田。依依榆柳之径。非若昌黎始来京国。勤半生而有庐。偶类摩诘晚居南山。缘中岁之好道。寻圣贤之所乐。承祖考之馀休。粗述儿郎之谣。聊相工师之役。儿郎伟抛梁东。山势崚嶒绕郭东。宛似故林回首处。石田茅屋涧之东。儿郎伟抛梁南。轩窗终日对终南。诗社秖今馀结习。何妨联句续城南。儿郎伟抛梁西。溪东扶杖到溪西。阛阓风尘浑不逼。横冈有意障村西。儿郎伟抛梁北。龙盘虎踞山从北。葱笼佳气拥 宸居。臣子精忱长拱北。儿郎伟抛梁上。晨夕云岚浮屋上。北窗长夏午
就静。实惬雅素之心。城市自有山林。人间之风日不到。闾巷殆同乡里。野外之习俗斯存。盖自离乱八十年来。莽为丘墟三四里许。人居稍稍还集。率多閒人。客驾时时入来。曾非俗客。况先人降生此地。而仲兄经纪宗家。宗族古所敦。幸多处于邻洞。兄弟毋胥远。咸欲聚于一坊。人称李氏之村。自乐棣华之咏。东阡南陌。父老杖屦之过从。暮诵朝吟。子弟文字之讲习。回瞻 北阙。路不迷于朝参。密迩先祠。诚可展于时荐。正寝厅事。既有内外之分。燠室凉堂。颇适起居之节。爰居爰处。苟美苟完。疏泉凿池。可玩徘徊光影。种花莳竹。只取怡养心神。历历瓜芋之田。依依榆柳之径。非若昌黎始来京国。勤半生而有庐。偶类摩诘晚居南山。缘中岁之好道。寻圣贤之所乐。承祖考之馀休。粗述儿郎之谣。聊相工师之役。儿郎伟抛梁东。山势崚嶒绕郭东。宛似故林回首处。石田茅屋涧之东。儿郎伟抛梁南。轩窗终日对终南。诗社秖今馀结习。何妨联句续城南。儿郎伟抛梁西。溪东扶杖到溪西。阛阓风尘浑不逼。横冈有意障村西。儿郎伟抛梁北。龙盘虎踞山从北。葱笼佳气拥 宸居。臣子精忱长拱北。儿郎伟抛梁上。晨夕云岚浮屋上。北窗长夏午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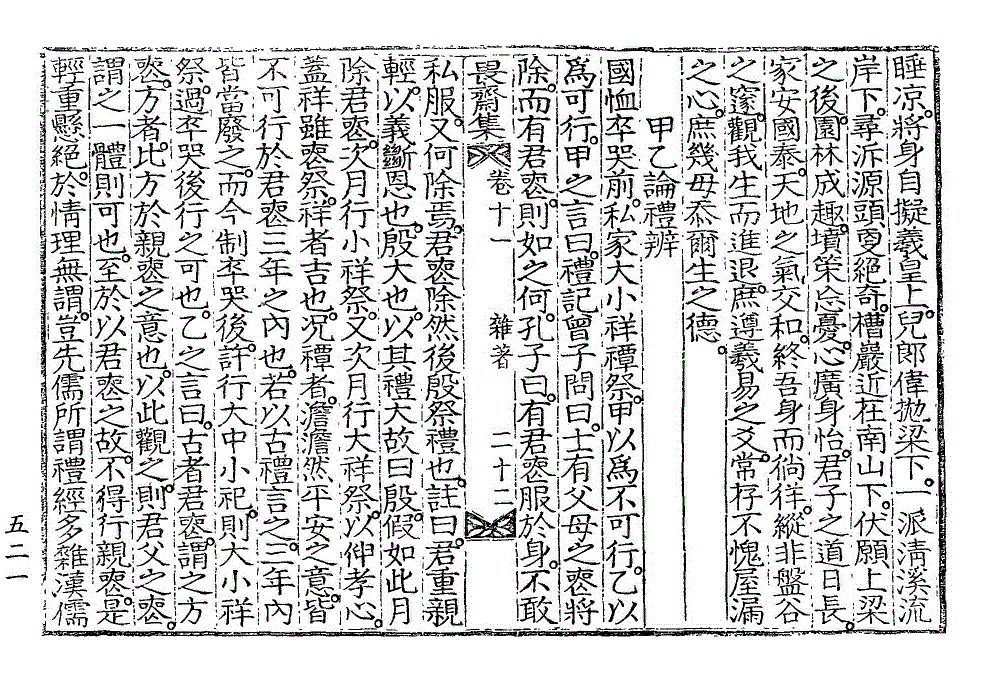 睡凉。将身自拟羲皇上。儿郎伟抛梁下。一派清溪流岸下。寻溯源头更绝奇。槽岩近在南山下。伏愿上梁之后。园林成趣。坟策忘忧。心广身怡。君子之道日长。家安国泰。天地之气交和。终吾身而徜徉。纵非盘谷之邃。观我生而进退。庶遵羲易之爻。常存不愧屋漏之心。庶几毋忝尔生之德。
睡凉。将身自拟羲皇上。儿郎伟抛梁下。一派清溪流岸下。寻溯源头更绝奇。槽岩近在南山下。伏愿上梁之后。园林成趣。坟策忘忧。心广身怡。君子之道日长。家安国泰。天地之气交和。终吾身而徜徉。纵非盘谷之邃。观我生而进退。庶遵羲易之爻。常存不愧屋漏之心。庶几毋忝尔生之德。甲乙论礼辨
国恤卒哭前。私家大小祥禫祭。甲以为不可行。乙以为可行。甲之言曰。礼记曾子问曰。士有父母之丧将除。而有君丧。则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君丧除然后殷祭礼也。注曰。君重亲轻。以义断恩也。殷大也。以其礼大故曰殷。假如此月除君丧。次月行小祥祭。又次月行大祥祭。以伸孝心。盖祥虽丧祭。祥者吉也。况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皆不可行于君丧三年之内也。若以古礼言之。三年内皆当废之。而今制卒哭后。许行大中小祀。则大小祥祭。过卒哭后行之可也。乙之言曰。古者君丧。谓之方丧。方者。比方于亲丧之意也。以此观之。则君父之丧。谓之一体则可也。至于以君丧之故。不得行亲丧。是轻重悬绝。于情理无谓。岂先儒所谓礼经多杂汉儒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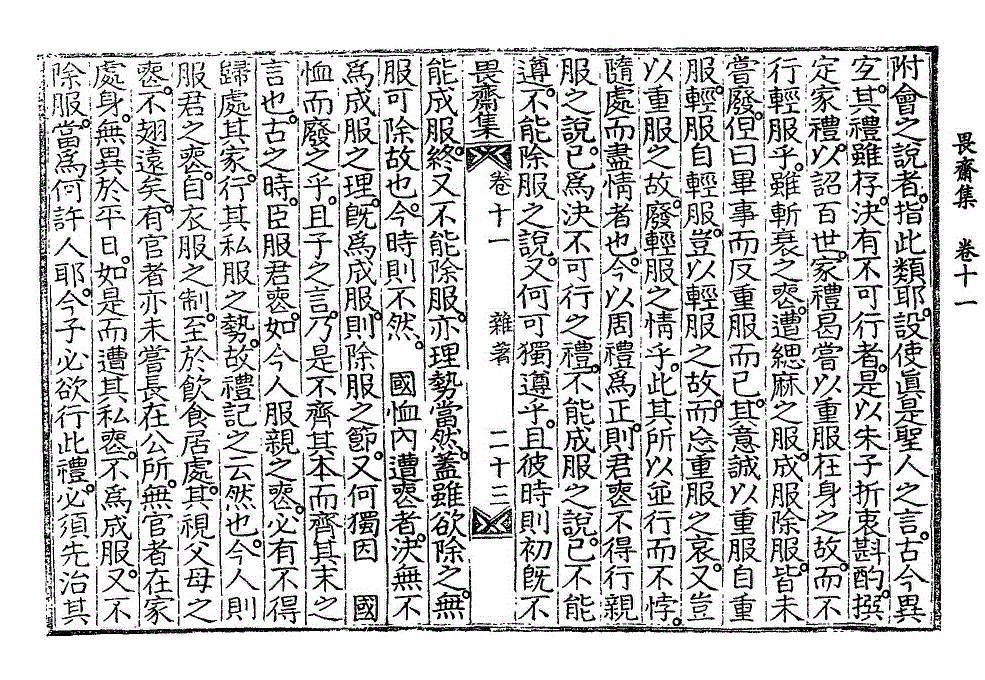 附会之说者。指此类耶。设使真是圣人之言。古今异宜。其礼虽存。决有不可行者。是以朱子折衷斟酌。撰定家礼。以诏百世。家礼曷尝以重服在身之故。而不行轻服乎。虽斩衰之丧。遭缌麻之服。成服除服。皆未尝废。但曰毕事而反重服而已。其意诚以重服自重服。轻服自轻服。岂以轻服之故。而忘重服之哀。又岂以重服之故。废轻服之情乎。此其所以并行而不悖。随处而尽情者也。今以周礼为正。则君丧不得行亲服之说。已为决不可行之礼。不能成服之说。已不能遵。不能除服之说。又何可独遵乎。且彼时则初既不能成服。终又不能除服。亦理势当然。盖虽欲除之。无服可除故也。今时则不然。 国恤内遭丧者。决无不为成服之理。既为成服。则除服之节。又何独因 国恤而废之乎。且子之言。乃是不齐其本而齐其末之言也。古之时。臣服君丧。如今人服亲之丧。必有不得归处其家。行其私服之势。故礼记之云然也。今人则服君之丧。自衣服之制。至于饮食居处。其视父母之丧。不翅远矣。有官者亦未尝长在公所。无官者在家处身。无异于平日。如是而遭其私丧。不为成服。又不除服。当为何许人耶。今子必欲行此礼。必须先治其
附会之说者。指此类耶。设使真是圣人之言。古今异宜。其礼虽存。决有不可行者。是以朱子折衷斟酌。撰定家礼。以诏百世。家礼曷尝以重服在身之故。而不行轻服乎。虽斩衰之丧。遭缌麻之服。成服除服。皆未尝废。但曰毕事而反重服而已。其意诚以重服自重服。轻服自轻服。岂以轻服之故。而忘重服之哀。又岂以重服之故。废轻服之情乎。此其所以并行而不悖。随处而尽情者也。今以周礼为正。则君丧不得行亲服之说。已为决不可行之礼。不能成服之说。已不能遵。不能除服之说。又何可独遵乎。且彼时则初既不能成服。终又不能除服。亦理势当然。盖虽欲除之。无服可除故也。今时则不然。 国恤内遭丧者。决无不为成服之理。既为成服。则除服之节。又何独因 国恤而废之乎。且子之言。乃是不齐其本而齐其末之言也。古之时。臣服君丧。如今人服亲之丧。必有不得归处其家。行其私服之势。故礼记之云然也。今人则服君之丧。自衣服之制。至于饮食居处。其视父母之丧。不翅远矣。有官者亦未尝长在公所。无官者在家处身。无异于平日。如是而遭其私丧。不为成服。又不除服。当为何许人耶。今子必欲行此礼。必须先治其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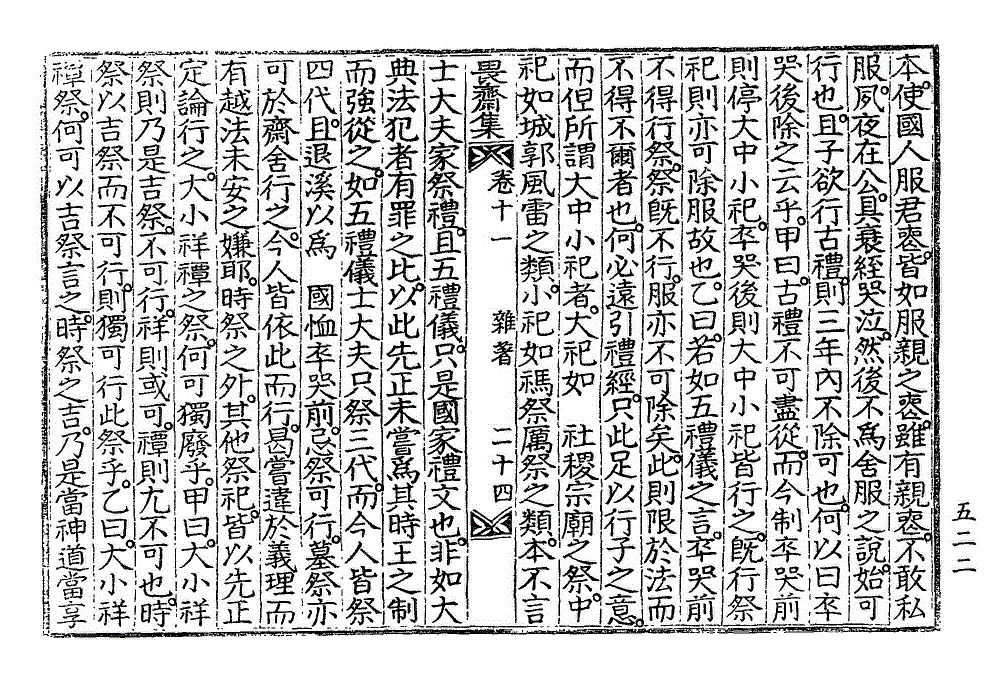 本。使国人服君丧。皆如服亲之丧。虽有亲丧。不敢私服。夙夜在公。具衰绖哭泣。然后不为舍服之说。始可行也。且子欲行古礼。则三年内不除可也。何以曰卒哭后除之云乎。甲曰。古礼不可尽从。而今制卒哭前则停大中小祀。卒哭后则大中小祀皆行之。既行祭祀则亦可除服故也。乙曰。若如五礼仪之言。卒哭前不得行祭。祭既不行。服亦不可除矣。此则限于法而不得不尔者也。何必远引礼经。只此足以行子之意。而但所谓大中小祀者。大祀如 社稷宗庙之祭。中祀如城郭风雷之类。小祀如祃祭厉祭之类。本不言士大夫家祭礼。且五礼仪。只是国家礼文也。非如大典法犯者有罪之比。以此先正未尝为其时王之制而强从之。如五礼仪士大夫只祭三代。而今人皆祭四代。且退溪以为 国恤卒哭前。忌祭可行。墓祭亦可于斋舍行之。今人皆依此而行。曷尝违于义理而有越法未安之嫌耶。时祭之外。其他祭祀。皆以先正定论行之。大小祥禫之祭。何可独废乎。甲曰。大小祥祭则乃是吉祭。不可行。祥则或可。禫则尤不可也。时祭以吉祭而不可行。则独可行此祭乎。乙曰。大小祥禫祭。何可以吉祭言之。时祭之吉。乃是当神道当享
本。使国人服君丧。皆如服亲之丧。虽有亲丧。不敢私服。夙夜在公。具衰绖哭泣。然后不为舍服之说。始可行也。且子欲行古礼。则三年内不除可也。何以曰卒哭后除之云乎。甲曰。古礼不可尽从。而今制卒哭前则停大中小祀。卒哭后则大中小祀皆行之。既行祭祀则亦可除服故也。乙曰。若如五礼仪之言。卒哭前不得行祭。祭既不行。服亦不可除矣。此则限于法而不得不尔者也。何必远引礼经。只此足以行子之意。而但所谓大中小祀者。大祀如 社稷宗庙之祭。中祀如城郭风雷之类。小祀如祃祭厉祭之类。本不言士大夫家祭礼。且五礼仪。只是国家礼文也。非如大典法犯者有罪之比。以此先正未尝为其时王之制而强从之。如五礼仪士大夫只祭三代。而今人皆祭四代。且退溪以为 国恤卒哭前。忌祭可行。墓祭亦可于斋舍行之。今人皆依此而行。曷尝违于义理而有越法未安之嫌耶。时祭之外。其他祭祀。皆以先正定论行之。大小祥禫之祭。何可独废乎。甲曰。大小祥祭则乃是吉祭。不可行。祥则或可。禫则尤不可也。时祭以吉祭而不可行。则独可行此祭乎。乙曰。大小祥禫祭。何可以吉祭言之。时祭之吉。乃是当神道当享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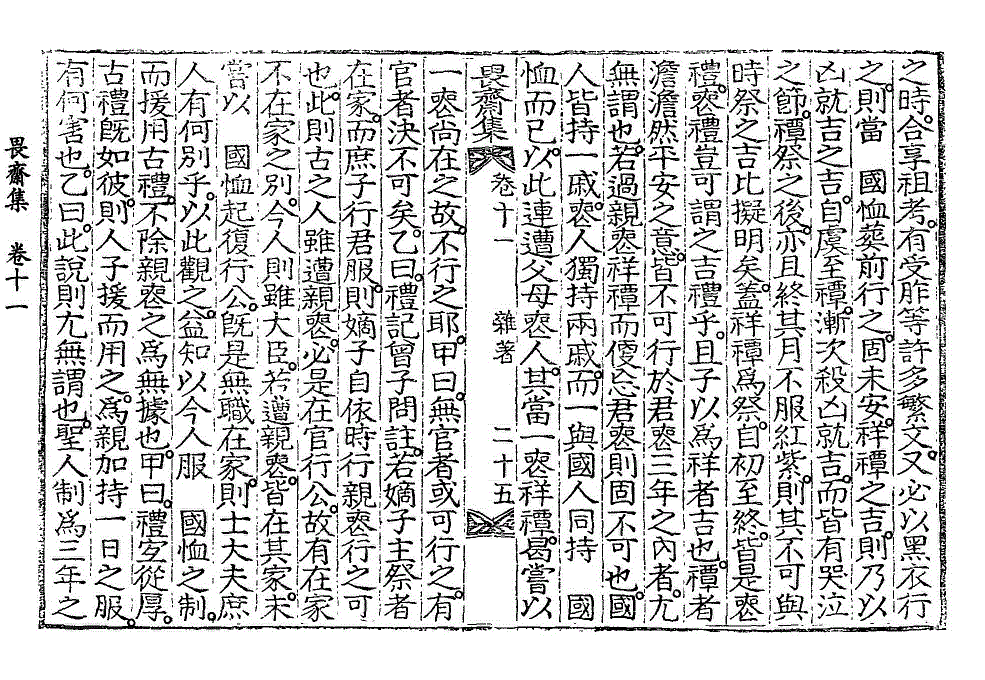 之时。合享祖考。有受胙等许多繁文。又必以黑衣行之。则当 国恤葬前行之。固未安。祥禫之吉。则乃以凶就吉之吉。自虞至禫。渐次杀凶就吉。而皆有哭泣之节。禫祭之后。亦且终其月不服红紫。则其不可与时祭之吉比拟明矣。盖祥禫为祭。自初至终。皆是丧礼。丧礼岂可谓之吉礼乎。且子以为祥者吉也。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皆不可行于君丧三年之内者。尤无谓也。若过亲丧祥禫而便忘君丧则固不可也。国人皆持一戚。丧人独持两戚。而一与国人同持 国恤而已。以此连遭父母丧人。其当一丧祥禫。曷尝以一丧尚在之故。不行之耶。甲曰。无官者或可行之。有官者决不可矣。乙曰。礼记曾子问注。若嫡子主祭者在家。而庶子行君服。则嫡子自依时行亲丧行之可也。此则古之人虽遭亲丧。必是在官行公。故有在家不在家之别。今人则虽大臣。若遭亲丧。皆在其家。未尝以 国恤起复行公。既是无职在家。则士大夫庶人有何别乎。以此观之。益知以今人服 国恤之制。而援用古礼。不除亲丧之为无据也。甲曰。礼宜从厚。古礼既如彼。则人子援而用之。为亲加持一日之服。有何害也。乙曰。此说则尤无谓也。圣人制为三年之
之时。合享祖考。有受胙等许多繁文。又必以黑衣行之。则当 国恤葬前行之。固未安。祥禫之吉。则乃以凶就吉之吉。自虞至禫。渐次杀凶就吉。而皆有哭泣之节。禫祭之后。亦且终其月不服红紫。则其不可与时祭之吉比拟明矣。盖祥禫为祭。自初至终。皆是丧礼。丧礼岂可谓之吉礼乎。且子以为祥者吉也。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皆不可行于君丧三年之内者。尤无谓也。若过亲丧祥禫而便忘君丧则固不可也。国人皆持一戚。丧人独持两戚。而一与国人同持 国恤而已。以此连遭父母丧人。其当一丧祥禫。曷尝以一丧尚在之故。不行之耶。甲曰。无官者或可行之。有官者决不可矣。乙曰。礼记曾子问注。若嫡子主祭者在家。而庶子行君服。则嫡子自依时行亲丧行之可也。此则古之人虽遭亲丧。必是在官行公。故有在家不在家之别。今人则虽大臣。若遭亲丧。皆在其家。未尝以 国恤起复行公。既是无职在家。则士大夫庶人有何别乎。以此观之。益知以今人服 国恤之制。而援用古礼。不除亲丧之为无据也。甲曰。礼宜从厚。古礼既如彼。则人子援而用之。为亲加持一日之服。有何害也。乙曰。此说则尤无谓也。圣人制为三年之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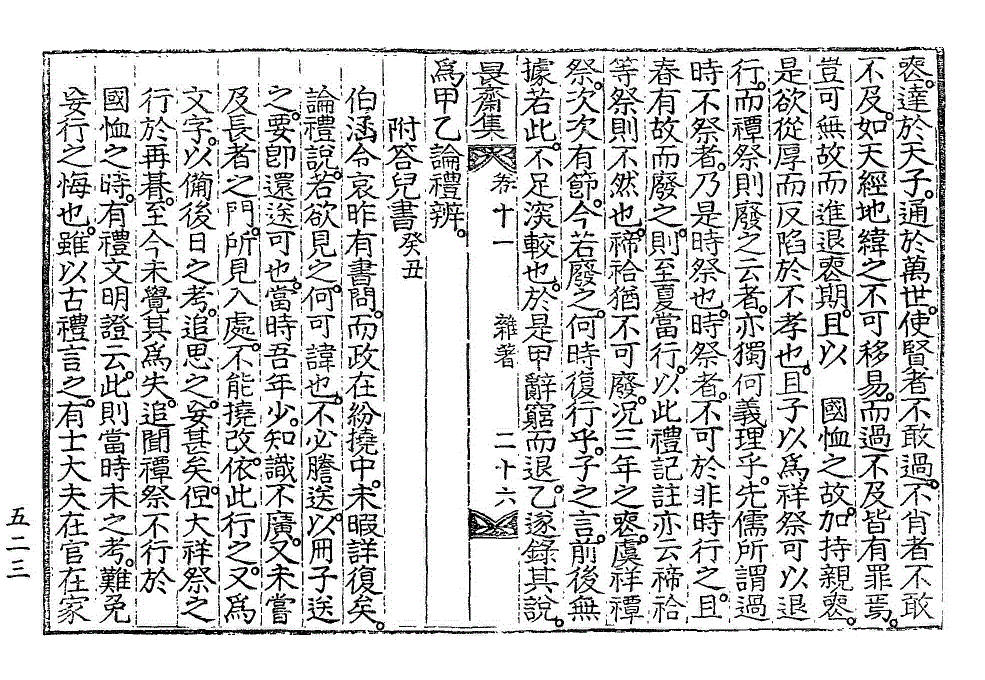 丧。达于天子。通于万世。使贤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如天经地纬之不可移易。而过不及皆有罪焉。岂可无故而进退丧期。且以 国恤之故。加持亲丧。是欲从厚而反陷于不孝也。且子以为祥祭可以退行。而禫祭则废之云者。亦独何义理乎。先儒所谓过时不祭者。乃是时祭也。时祭者。不可于非时行之。且春有故而废之。则至夏当行。以此礼记注亦云禘祫等祭则不然也。禘祫犹不可废。况三年之丧。虞祥禫祭。次次有节。今若废之。何时复行乎。子之言。前后无据若此。不足深较也。于是甲辞穷而退。乙遂录其说。为甲乙论礼辨。
丧。达于天子。通于万世。使贤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如天经地纬之不可移易。而过不及皆有罪焉。岂可无故而进退丧期。且以 国恤之故。加持亲丧。是欲从厚而反陷于不孝也。且子以为祥祭可以退行。而禫祭则废之云者。亦独何义理乎。先儒所谓过时不祭者。乃是时祭也。时祭者。不可于非时行之。且春有故而废之。则至夏当行。以此礼记注亦云禘祫等祭则不然也。禘祫犹不可废。况三年之丧。虞祥禫祭。次次有节。今若废之。何时复行乎。子之言。前后无据若此。不足深较也。于是甲辞穷而退。乙遂录其说。为甲乙论礼辨。附答儿书(癸丑)
伯涵令哀昨有书问。而政在纷挠中。未暇详复矣。论礼说。若欲见之。何可讳也。不必誊送。以册子送之。要即还送可也。当时吾年少。知识不广。又未尝及长者之门。所见入处。不能挠改。依此行之。又为文字。以备后日之考。追思之。妄甚矣。但大祥祭之行于再期。至今未觉其为失。追闻禫祭不行于 国恤之时。有礼文明證云。此则当时未之考。难免妄行之悔也。虽以古礼言之。有士大夫在官在家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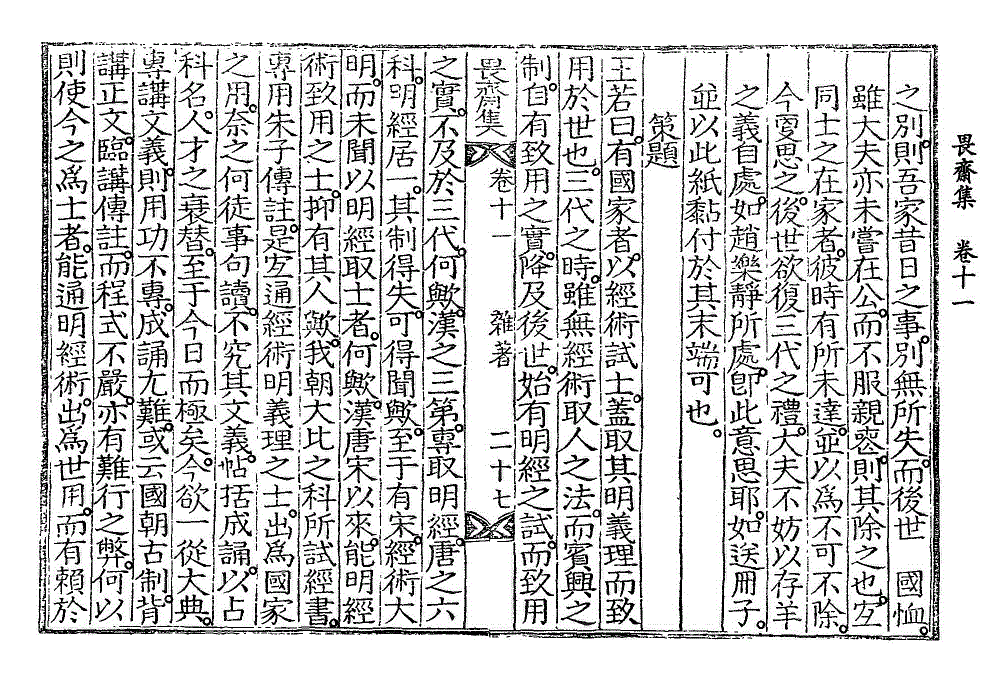 之别。则吾家昔日之事。别无所失。而后世 国恤。虽大夫亦未尝在公。而不服亲丧。则其除之也。宜同士之在家者。彼时有所未达。并以为不可不除。今更思之。后世欲复三代之礼。大夫不妨以存羊之义自处。如赵乐静所处。即此意思耶。如送册子。并以此纸黏付于其末端可也。
之别。则吾家昔日之事。别无所失。而后世 国恤。虽大夫亦未尝在公。而不服亲丧。则其除之也。宜同士之在家者。彼时有所未达。并以为不可不除。今更思之。后世欲复三代之礼。大夫不妨以存羊之义自处。如赵乐静所处。即此意思耶。如送册子。并以此纸黏付于其末端可也。策题
王若曰。有国家者。以经术试士。盖取其明义理而致用于世也。三代之时。虽无经术取人之法。而宾兴之制。自有致用之实。降及后世。始有明经之试。而致用之实。不及于三代。何欤。汉之三第。专取明经。唐之六科。明经居一。其制得失。可得闻欤。至于有宋。经术大明。而未闻以明经取士者。何欤。汉唐宋以来。能明经术致用之士。抑有其人欤。我朝大比之科所试经书。专用朱子传注。是宜通经术明义理之士。出为国家之用。奈之何徒事句读。不究其文义。帖括成诵。以占科名。人才之衰替。至于今日而极矣。今欲一从大典。专讲文义。则用功不专。成诵尤难。或云国朝古制。背讲正文。临讲传注。而程式不严。亦有难行之弊。何以则使今之为士者。能通明经术。出为世用。而有赖于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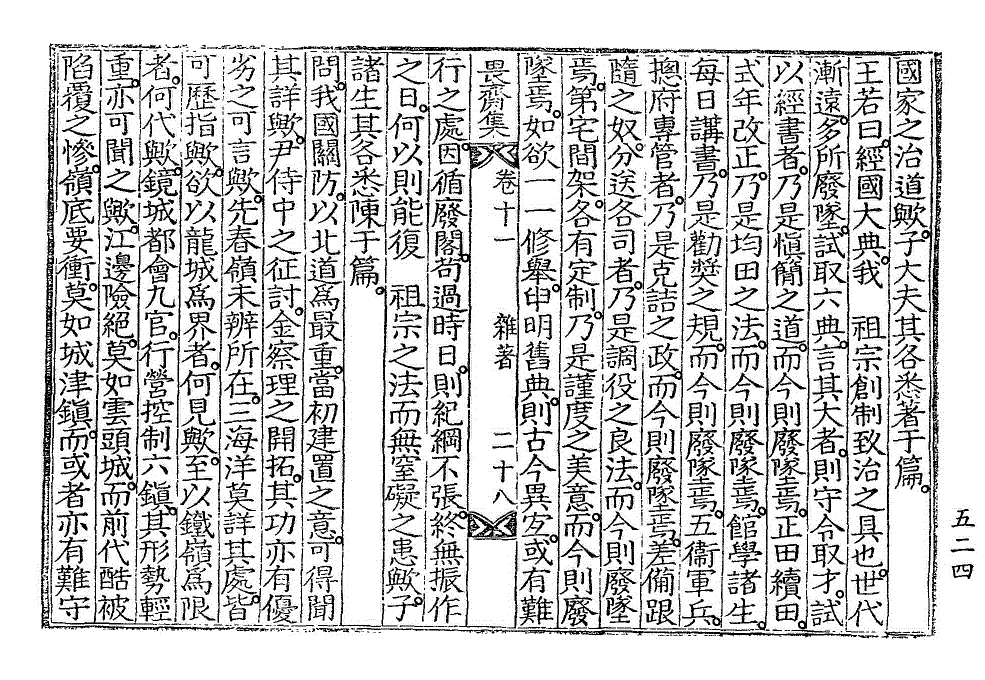 国家之治道欤。子大夫其各悉著于篇。
国家之治道欤。子大夫其各悉著于篇。王若曰。经国大典。我 祖宗创制致治之具也。世代渐远。多所废坠。试取六典。言其大者。则守令取才。试以经书者。乃是慎简之道。而今则废坠焉。正田续田。式年改正。乃是均田之法。而今则废坠焉。馆学诸生。每日讲书。乃是劝奖之规。而今则废坠焉。五卫军兵。总府专管者。乃是克诘之政。而今则废坠焉。差备跟随之奴。分送各司者。乃是调役之良法。而今则废坠焉。第宅间架。各有定制。乃是谨度之美意。而今则废坠焉。如欲一一修举。申明旧典。则古今异宜。或有难行之处。因循废阁。苟过时日。则纪纲不张。终无振作之日。何以则能复 祖宗之法而无窒碍之患欤。子诸生其各悉陈于篇。
问。我国关防。以北道为最重。当初建置之意。可得闻其详欤。尹侍中之征讨。金察理之开拓。其功亦有优劣之可言欤。先春岭未辨所在。三海洋莫详其处。皆可历指欤。欲以龙城为界者。何见欤。至以铁岭为限者。何代欤。镜城都会九官。行营控制六镇。其形势轻重。亦可闻之欤。江边险绝。莫如云头城。而前代酷被陷覆之惨。岭底要冲。莫如城津镇。而或者亦有难守
畏斋集卷之十一 第 5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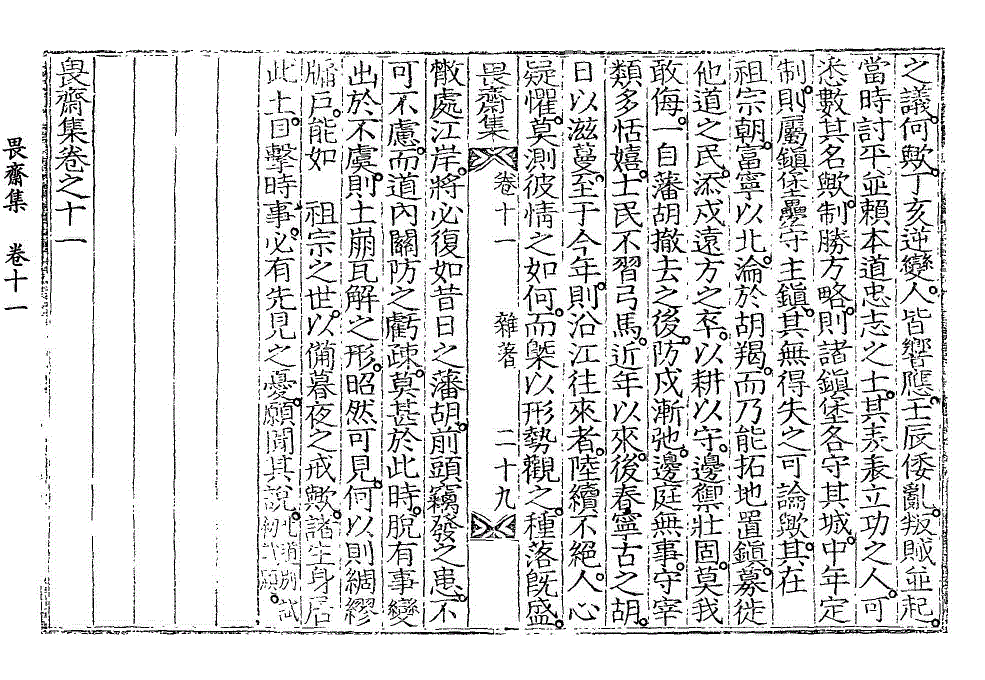 之议。何欤。丁亥逆变。人皆响应。壬辰倭乱。叛贼并起。当时讨平。并赖本道忠志之士。其表表立功之人。可悉数其名欤。制胜方略。则诸镇堡各守其城。中年定制。则属镇堡叠守主镇。其无得失之可论欤。其在 祖宗朝。富宁以北。沦于胡羯。而乃能拓地置镇。募徙他道之民。添戍远方之卒。以耕以守。边御壮固。莫我敢侮。一自藩胡撤去之后。防戍渐弛。边庭无事。守宰类多恬嬉。士民不习弓马。近年以来。后春,宁古之胡。日以滋蔓。至于今年。则沿江往来者。陆续不绝。人心疑惧。莫测彼情之如何。而槩以形势观之。种落既盛。散处江岸。将必复如昔日之藩胡。前头窃发之患。不可不虑。而道内关防之亏疏。莫甚于此时。脱有事变出于不虞。则土崩瓦解之形。昭然可见。何以则绸缪牖户。能如 祖宗之世。以备暮夜之戒欤。诸生身居此土。目击时事。必有先见之忧。愿闻其说。(北道别试初试题。)
之议。何欤。丁亥逆变。人皆响应。壬辰倭乱。叛贼并起。当时讨平。并赖本道忠志之士。其表表立功之人。可悉数其名欤。制胜方略。则诸镇堡各守其城。中年定制。则属镇堡叠守主镇。其无得失之可论欤。其在 祖宗朝。富宁以北。沦于胡羯。而乃能拓地置镇。募徙他道之民。添戍远方之卒。以耕以守。边御壮固。莫我敢侮。一自藩胡撤去之后。防戍渐弛。边庭无事。守宰类多恬嬉。士民不习弓马。近年以来。后春,宁古之胡。日以滋蔓。至于今年。则沿江往来者。陆续不绝。人心疑惧。莫测彼情之如何。而槩以形势观之。种落既盛。散处江岸。将必复如昔日之藩胡。前头窃发之患。不可不虑。而道内关防之亏疏。莫甚于此时。脱有事变出于不虞。则土崩瓦解之形。昭然可见。何以则绸缪牖户。能如 祖宗之世。以备暮夜之戒欤。诸生身居此土。目击时事。必有先见之忧。愿闻其说。(北道别试初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