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x 页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遗事
遗事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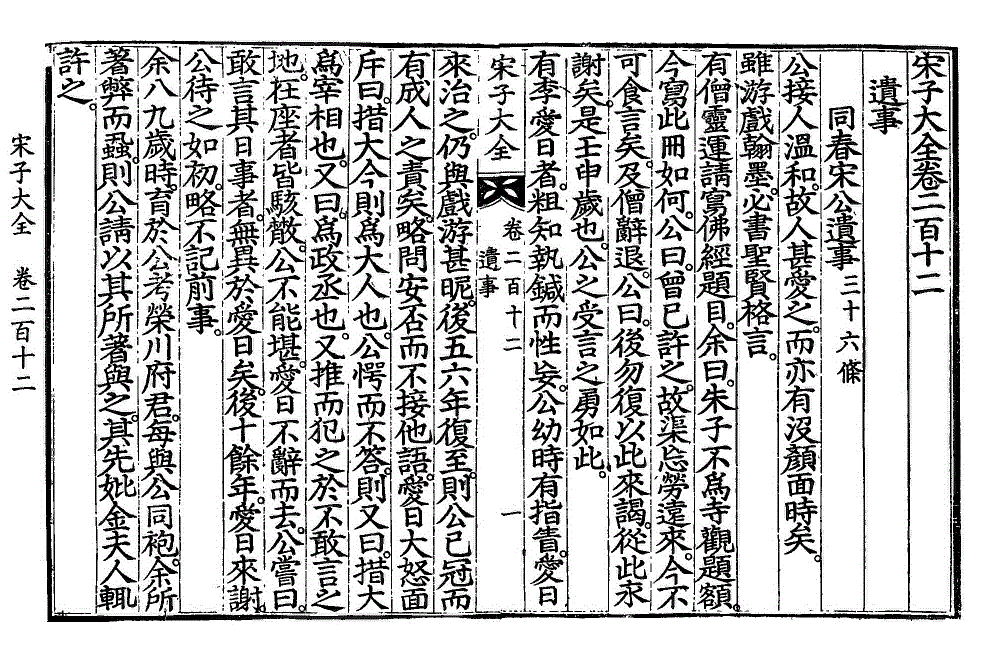 同春宋公遗事(三十六条)
同春宋公遗事(三十六条)公接人温和。故人甚爱之。而亦有没颜面时矣。
虽游戏翰墨。必书圣贤格言。
有僧灵运请写佛经题目。余曰。朱子不为寺观题额。今写此册如何。公曰。曾已许之。故渠忘劳远来。今不可食言矣。及僧辞退。公曰。后勿复以此来谒。从此永谢矣。是壬申岁也。公之受言之勇如此。
有李爱日者。粗知执针而性妄。公幼时有指眚。爱日来治之。仍与戏游甚昵。后五六年复至。则公已冠而有成人之责矣。略问安否而不接他语。爱日大怒面斥曰。措大今则为大人也。公愕而不答。则又曰。措大为宰相也。又曰。为政丞也。又推而犯之于不敢言之地。在座者皆骇散。公不能堪。爱日不辞而去。公尝曰。敢言其日事者。无异于爱日矣。后十馀年。爱日来谢。公待之如初。略不记前事。
余八九岁时。育于公考荣川府君。每与公同袍。余所著弊而虱。则公请以其所著与之。其先妣金夫人辄许之。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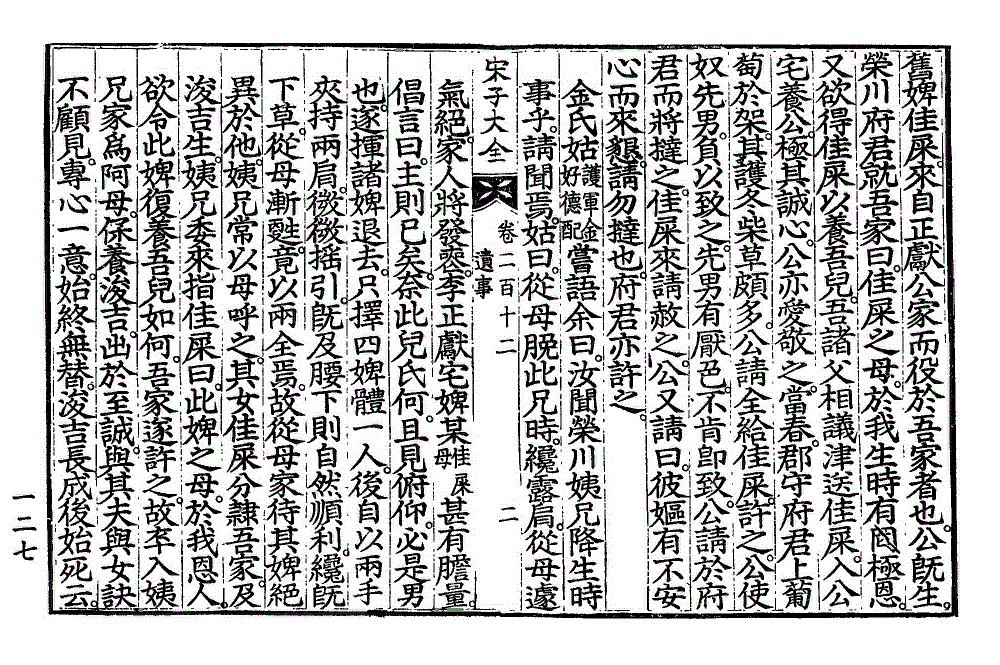 旧婢佳屎。来自正献公家而役于吾家者也。公既生。荣川府君就吾家曰。佳屎之母。于我生时有罔极恩。又欲得佳屎以养吾儿。吾诸父相议津送佳屎。入公宅养公。极其诚心。公亦爱敬之。当春。郡守府君上葡萄于架。其护冬柴草颇多。公请全给佳屎。许之。公使奴先男。负以致之。先男有厌色。不肯即致。公请于府君而将挞之。佳屎来请赦之。公又请曰。彼妪有不安心而来恳。请勿挞也。府君亦许之。
旧婢佳屎。来自正献公家而役于吾家者也。公既生。荣川府君就吾家曰。佳屎之母。于我生时有罔极恩。又欲得佳屎以养吾儿。吾诸父相议津送佳屎。入公宅养公。极其诚心。公亦爱敬之。当春。郡守府君上葡萄于架。其护冬柴草颇多。公请全给佳屎。许之。公使奴先男。负以致之。先男有厌色。不肯即致。公请于府君而将挞之。佳屎来请赦之。公又请曰。彼妪有不安心而来恳。请勿挞也。府君亦许之。金氏姑(护军金好德配)尝语余曰。汝闻荣川姨兄降生时事乎。请闻焉。姑曰。从母晚此兄时。才露肩。从母遽气绝。家人将发丧。李正献宅婢某(佳屎母)甚有胆量。倡言曰。主则已矣。奈此儿氏何。且见俯仰。必是男也。遂挥诸婢退去。只择四婢体一人。后自以两手夹持两肩。微微摇引。既及腰下则自然顺利。才既下草。从母渐苏。竟以两全焉。故从母家待其婢绝异于他。姨兄常以母呼之。其女佳屎分隶吾家。及浚吉生。姨兄委来指佳屎曰。此婢之母。于我恩人。欲令此婢复养吾儿如何。吾家遂许之。故卒入姨兄家为阿母。保养浚吉。出于至诚。与其夫与女诀不顾见。专心一意。始终无替。浚吉长成后始死云。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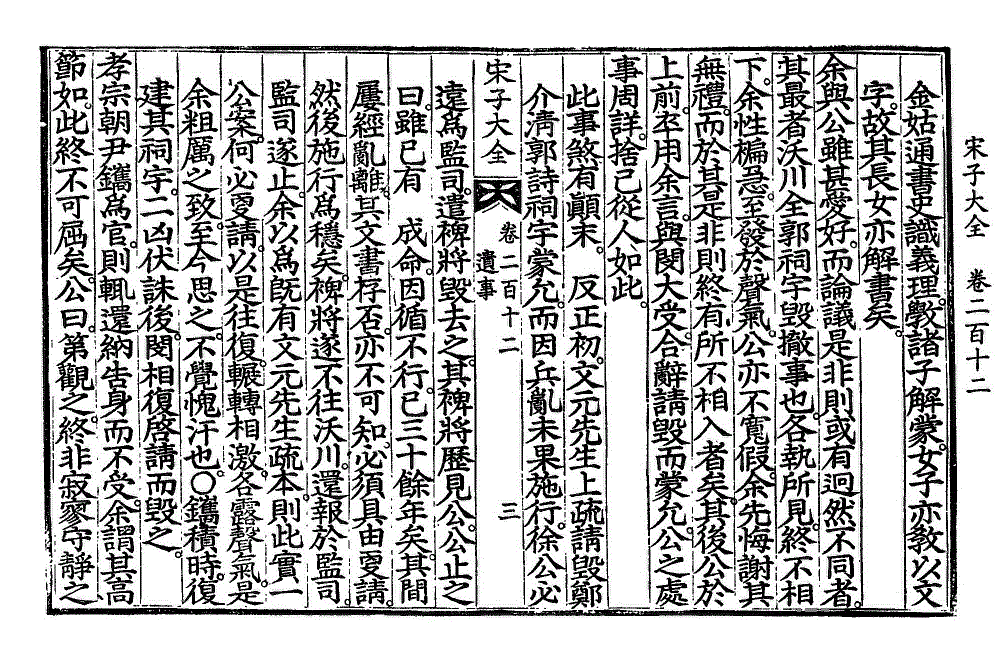 金姑通书史识义理。敩诸子解蒙。女子亦教以文字。故其长女亦解书矣。
金姑通书史识义理。敩诸子解蒙。女子亦教以文字。故其长女亦解书矣。余与公虽甚爱好。而论议是非则或有迥然不同者。其最者沃川全郭祠宇毁撤事也。各执所见。终不相下。余性褊急。至发于声气。公亦不宽假。余先悔谢其无礼。而于其是非则终有所不相入者矣。其后公于上前。卒用余言。与闵大受。合辞请毁而蒙允。公之处事周详。舍己从人如此。
此事煞有颠末。 反正初。文元先生上疏请毁郑介清郭诗祠宇蒙允。而因兵乱未果施行。徐公必远为监司。遣裨将毁去之。其裨将历见公。公止之曰。虽已有 成命。因循不行。已三十馀年矣。其间屡经乱离。其文书存否。亦不可知。必须具由更请。然后施行为稳矣。裨将遂不往沃川。还报于监司。监司遂止。余以为既有文元先生疏本。则此实一公案。何必更请。以是往复。辗转相激。各露声气。是余粗厉之致。至今思之。不觉愧汗也。○鑴,积时。复建其祠宇。二凶伏诛后。闵相复启请而毁之。
孝宗朝尹鑴为官。则辄还纳告身而不受。余谓其高节如此。终不可屈矣。公曰。第观之。终非寂寥守静之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28L 页
 人也。至今十七年而果验。昔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同省殷浩。见其有确然之志。王谢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刘曰卿辈真忧深源不起耶。其后浩果起而大狼狈。公之识度。真不愧于古人矣。
人也。至今十七年而果验。昔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同省殷浩。见其有确然之志。王谢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刘曰卿辈真忧深源不起耶。其后浩果起而大狼狈。公之识度。真不愧于古人矣。戊戌。同入 榻前。公曰。 宗庙所用祝差谬。又宗器不如法。请令某勘定。余进曰。臣固非其人。纵使实有此才具。窃恐此非今日急务。昔诸葛治蜀。不置史官。朱子论庙制不如古而曰。请兴复之后。还返旧都而一新之。以正千载之谬。 上竟不允公言。公出而见责曰。不料论议之相异如此也。吾意以为国之大事在戎与祀。今祀典之灭裂如此。欲望 祖宗垂佑锡羡于无穷。得乎。余曰。自 上既曰大计已定。则自此之后当权置百为。一意于此。而不可使精神分岐。然后可庶几焉。公曰。此当并行而不可偏废者也。余曰。上殿未尝苟同。下殿未尝失色。此古人之善事。吾辈共当勉之也。(闻 宗庙祝辞。以用于 太祖者。移用于 列圣。故所称功德。绝不相应云矣。)己丑年间。在都下。尝谓余曰。闵仲集福人也。其第三子亦甚佳。时持叔甚少也。
余外妹金氏。为李都事荣先妻。生二子圣锡,范锡。一日有人来传曰。金氏丧子矣。余惊曰。谁欤。公曰。必是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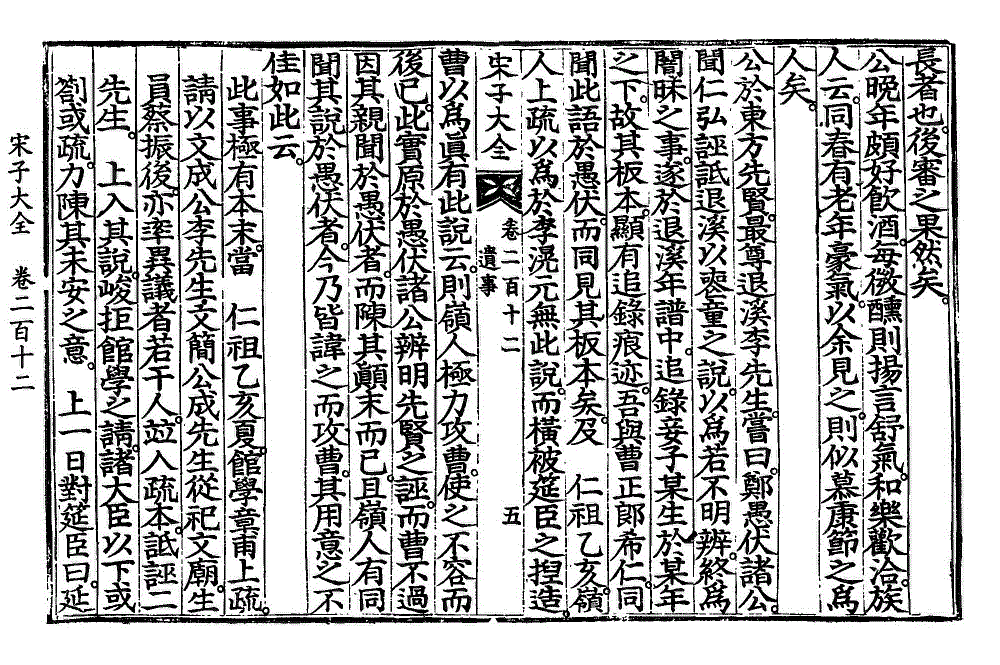 长者也。后审之果然矣。
长者也。后审之果然矣。公晚年颇好饮酒。每微醺则扬言舒气。和乐欢洽。族人云。同春有老年豪气。以余见之。则似慕康节之为人矣。
公于东方先贤。最尊退溪李先生。尝曰。郑愚伏诸公。闻仁弘诬诋退溪以丧童之说。以为若不明辨。终为闇昧之事。遂于退溪年谱中。追录妾子某生于某年之下。故其板本。显有追录痕迹。吾与曹正郎希仁。同闻此语于愚伏。而同见其板本矣。及 仁祖乙亥。岭人上疏以为于李滉元无此说。而横被筵臣之捏造。曹以为真有此说云。则岭人极力攻曹。使之不容而后已。此实原于愚伏诸公辨明先贤之诬。而曹不过因其亲闻于愚伏者。而陈其颠末而已。且岭人有同闻其说于愚伏者。今乃皆讳之而攻曹。其用意之不佳如此云。
此事极有本末。当 仁祖乙亥夏。馆学章甫上疏。请以文成公李先生,文简公成先生从祀文庙。生员蔡振后。亦率异议者若干人。并入疏本。诋诬二先生。 上入其说。峻拒馆学之请。诸大臣以下或劄或疏。力陈其未安之意。 上一日对筵臣曰。延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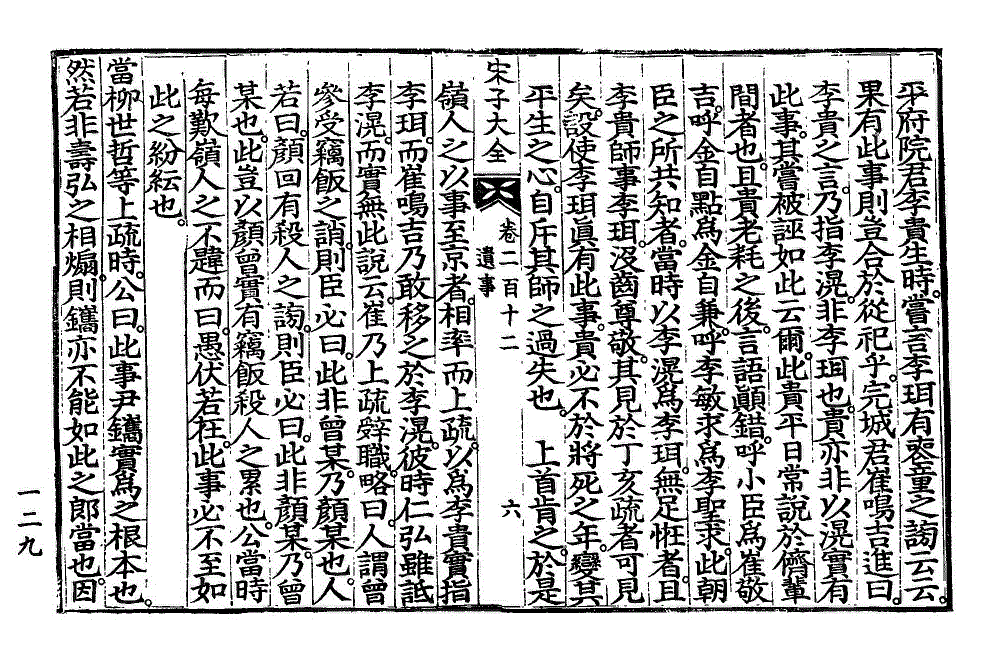 平府院君李贵生时。尝言李珥有丧童之谤云云。果有此事则岂合于从祀乎。完城君崔鸣吉进曰。李贵之言。乃指李滉。非李珥也。贵亦非以滉实有此事。其尝被诬如此云尔。此贵平日常说于侪辈间者也。且贵老耗之后。言语颠错。呼小臣为崔敬吉。呼金自点为金自兼。呼李敏求为李圣求。此朝臣之所共知者。当时以李滉为李珥。无足怪者。且李贵师事李珥。没齿尊敬。其见于丁亥疏者可见矣。设使李珥真有此事。贵必不于将死之年。变其平生之心。自斥其师之过失也。 上首肯之。于是岭人之以事至京者。相率而上疏。以为李贵实指李珥。而崔鸣吉乃敢移之于李滉。彼时仁弘虽诋李滉。而实无此说云。崔乃上疏辞职。略曰。人谓曾参受窃饭之诮。则臣必曰。此非曾某。乃颜某也。人若曰。颜回有杀人之谤。则臣必曰。此非颜某。乃曾某也。此岂以颜曾实有窃饭杀人之累也。公当时每叹岭人之不韪而曰。愚伏若在。此事必不至如此之纷纭也。
平府院君李贵生时。尝言李珥有丧童之谤云云。果有此事则岂合于从祀乎。完城君崔鸣吉进曰。李贵之言。乃指李滉。非李珥也。贵亦非以滉实有此事。其尝被诬如此云尔。此贵平日常说于侪辈间者也。且贵老耗之后。言语颠错。呼小臣为崔敬吉。呼金自点为金自兼。呼李敏求为李圣求。此朝臣之所共知者。当时以李滉为李珥。无足怪者。且李贵师事李珥。没齿尊敬。其见于丁亥疏者可见矣。设使李珥真有此事。贵必不于将死之年。变其平生之心。自斥其师之过失也。 上首肯之。于是岭人之以事至京者。相率而上疏。以为李贵实指李珥。而崔鸣吉乃敢移之于李滉。彼时仁弘虽诋李滉。而实无此说云。崔乃上疏辞职。略曰。人谓曾参受窃饭之诮。则臣必曰。此非曾某。乃颜某也。人若曰。颜回有杀人之谤。则臣必曰。此非颜某。乃曾某也。此岂以颜曾实有窃饭杀人之累也。公当时每叹岭人之不韪而曰。愚伏若在。此事必不至如此之纷纭也。当柳世哲等上疏时。公曰。此事尹鑴实为之根本也。然若非寿弘之相煽。则鑴亦不能如此之郎当也。因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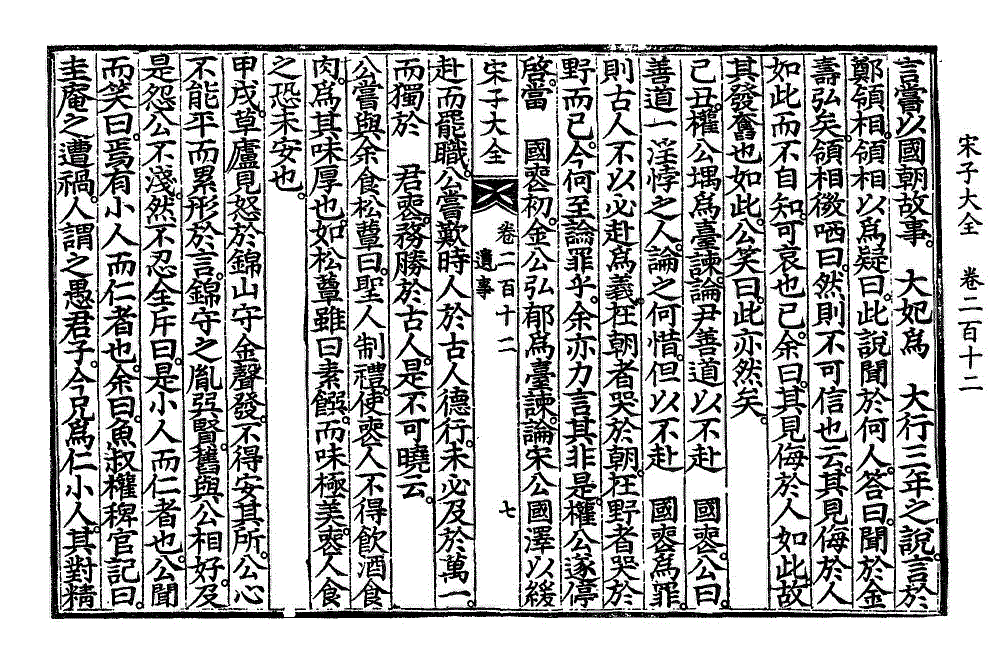 言尝以国朝故事。 大妃为 大行三年之说。言于郑领相。领相以为疑曰。此说闻于何人。答曰。闻于金寿弘矣。领相微哂曰。然则不可信也云。其见侮于人如此而不自知。可哀也已。余曰。其见侮于人如此。故其发奋也如此。公笑曰。此亦然矣。
言尝以国朝故事。 大妃为 大行三年之说。言于郑领相。领相以为疑曰。此说闻于何人。答曰。闻于金寿弘矣。领相微哂曰。然则不可信也云。其见侮于人如此而不自知。可哀也已。余曰。其见侮于人如此。故其发奋也如此。公笑曰。此亦然矣。己丑。权公堣为台谏。论尹善道以不赴 国丧。公曰。善道一淫悖之人。论之何惜。但以不赴 国丧为罪。则古人不以必赴为义。在朝者哭于朝。在野者哭于野而已。今何至论罪乎。余亦力言其非是。权公遂停启。当 国丧初。金公弘郁为台谏。论宋公国泽以缓赴而罢职。公尝叹时人于古人德行。未必及于万一。而独于 君丧。务胜于古人。是不可晓云。
公尝与余食松蕈曰。圣人制礼。使丧人不得饮酒食肉。为其味厚也。如松蕈虽曰素馔。而味极美。丧人食之恐未安也。
甲戌。草庐见怒于锦山守金声发。不得安其所。公心不能平而累形于言。锦守之胤巽贤。旧与公相好。及是怨公不浅。然不忍全斥曰。是小人而仁者也。公闻而笑曰。焉有小人而仁者也。余曰。鱼叔权稗官记曰。圭庵之遭祸。人谓之愚君子。今兄为仁小人。其对精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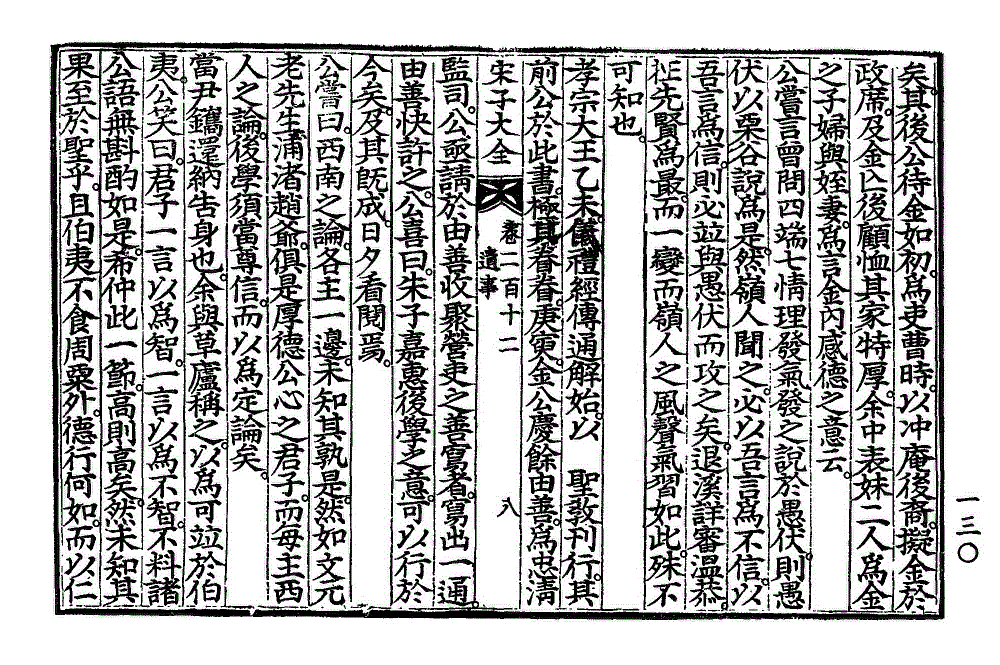 矣。其后公待金如初。为吏曹时。以冲庵后裔。拟金于政席。及金亡后顾恤其家特厚。余中表妹二人为金之子妇与侄妻。为言金内感德之意云。
矣。其后公待金如初。为吏曹时。以冲庵后裔。拟金于政席。及金亡后顾恤其家特厚。余中表妹二人为金之子妇与侄妻。为言金内感德之意云。公尝言曾问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说于愚伏。则愚伏以栗谷说为是。然岭人闻之。必以吾言为不信。以吾言为信。则必并与愚伏而攻之矣。退溪详审温恭。在先贤为最。而一变而岭人之风声气习如此。殊不可知也。
孝宗大王乙未。仪礼经传通解始。以 圣教刊行。其前公于此书。极其眷眷。庚寅。金公庆馀由善。为忠清监司。公亟请于由善收聚营吏之善写者。写出一通。由善快许之。公喜曰。朱子嘉惠后学之意。可以行于今矣。及其既成。日夕看阅焉。
公尝曰。西南之论。各主一边。未知其孰是。然如文元老先生,浦渚赵爷。俱是厚德公心之君子。而每主西人之论。后学须当尊信。而以为定论矣。
当尹鑴还纳告身也。余与草庐称之。以为可并于伯夷。公笑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不料诸公语无斟酌如是。希仲此一节。高则高矣。然未知其果至于圣乎。且伯夷不食周粟外。德行何如。而以仁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1H 页
 见称于孔子耶。余曰非谓全体。特以一节言之。公曰。虽以一节言之。须至饿死然后言之未晚也。(仍言其为尹以钦服丧之事。)
见称于孔子耶。余曰非谓全体。特以一节言之。公曰。虽以一节言之。须至饿死然后言之未晚也。(仍言其为尹以钦服丧之事。)宋得弼。尝以其曾祖同知公命。致言于公曰。怀德宰将至吾家。须来会叙话云。公责之曰。长者之言果如是耶。长者必曰城主。而汝乃曰怀德宰。何如是不逊耶。
学史略时。荣川府君问曰。人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是何故有此三者之异耶。公对曰。有严威则人不敢欺。是畏之也。有仁心则人不忍欺。是心服也。有智术则人不能欺。是服其明也。府君曰。然则孰优。对曰。不忍者上也。不能者次也。不敢者下也。府君大奇之。余先君子每访荣川府君。而归语不肖曰。每见某。必见其长进矣。是十岁时也。
公尝曰。人间万事。莫如有好子孙也。
己卯岁。谓曰。尹铿以黄口小儿。乃敢褒贬先贤。瑕谪退栗之论。至于牛溪则直斥其字。又已有著书垂后之意。无论其说之如何。而其气象浅促矣。其能久远乎。铿后改名鑴者也。
孝庙癸巳。吾宗为柳祖妣乞恩也。只据墓表数行文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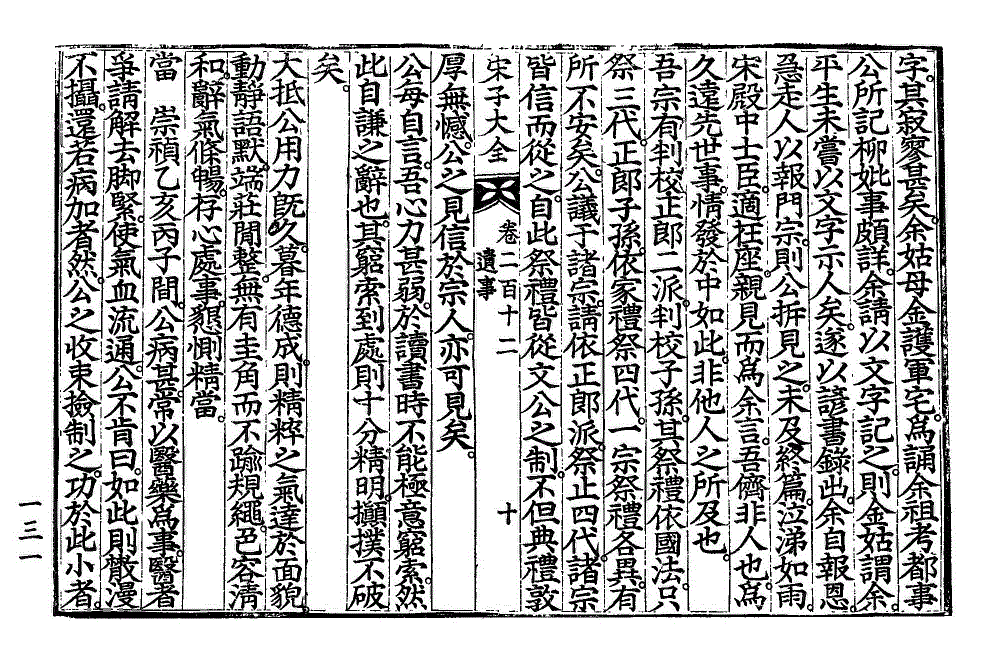 字。其寂寥甚矣。余姑母金护军宅。为诵余祖考都事公所记柳妣事颇详。余请以文字记之。则金姑谓余。平生未尝以文字示人矣。遂以谚书录出。余自报恩。急走人以报门宗。则公拆见之。未及终篇。泣涕如雨。宋殿中士臣。适在座。亲见而为余言。吾侪非人也。为久远先世事。情发于中如此。非他人之所及也。
字。其寂寥甚矣。余姑母金护军宅。为诵余祖考都事公所记柳妣事颇详。余请以文字记之。则金姑谓余。平生未尝以文字示人矣。遂以谚书录出。余自报恩。急走人以报门宗。则公拆见之。未及终篇。泣涕如雨。宋殿中士臣。适在座。亲见而为余言。吾侪非人也。为久远先世事。情发于中如此。非他人之所及也。吾宗有判校,正郎二派。判校子孙。其祭礼依国法。只祭三代。正郎子孙。依家礼祭四代。一宗祭礼各异。有所不安矣。公议于诸宗。请依正郎派。祭止四代。诸宗皆信而从之。自此祭礼皆从文公之制。不但典礼敦厚无憾。公之见信于宗人。亦可见矣。
公每自言。吾心力甚弱。于读书时不能极意穷索。然此自谦之辞也。其穷索到处则十分精明。攧扑不破矣。
大抵公用力既久。暮年德成。则精粹之气达于面貌。动静语默。端庄閒整。无有圭角而不踰规绳。色容清和。辞气条畅。存心处事。恳恻精当。
当 崇祯乙亥丙子间。公病甚。常以医药为事。医者争请解去脚紧。使气血流通。公不肯曰。如此则散漫不摄。还若病加者然。公之收束捡制之。功于此小者。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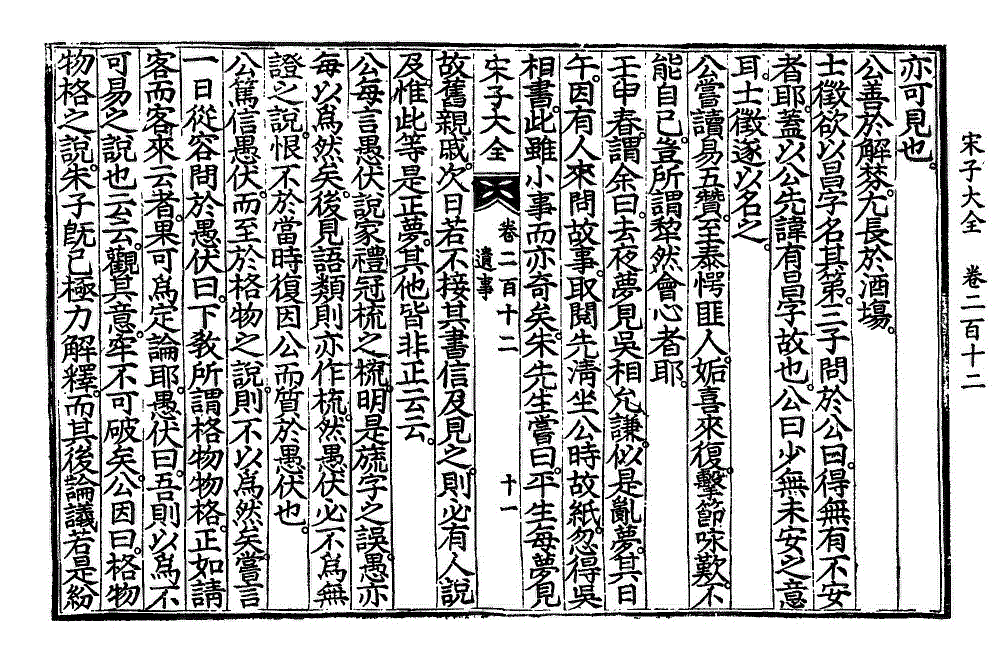 亦可见也。
亦可见也。公善于解棼。尤长于酒场。
士徵欲以昌字名其第。三子问于公曰。得无有不安者耶。盖以公先讳有昌字故也。公曰少无未安之意耳。士徵遂以名之。
公尝读易五赞。至泰愕匪人。姤喜来复。击节咏叹。不能自已。岂所谓犁然会心者耶。
壬申春。谓余曰。去夜梦见吴相允谦。似是乱梦。其日午。因有人来问故事。取阅先清坐公时故纸。忽得吴相书。此虽小事而亦奇矣。朱先生尝曰。平生每梦见故旧亲戚。次日若不接其书信及见之。则必有人说及。惟此等是正梦。其他皆非正云云。
公每言愚伏说家礼冠梳之梳。明是旒字之误。愚亦每以为然矣。后见语类则亦作梳。然愚伏必不为无證之说。恨不于当时复因公而质于愚伏也。
公笃信愚伏。而至于格物之说。则不以为然矣。尝言一日从容问于愚伏曰。下教所谓格物物格。正如请客而客来云者。果可为定论耶。愚伏曰。吾则以为不可易之说也云云。观其意。牢不可破矣。公因曰。格物物格之说。朱子既已极力解释。而其后论议若是纷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2L 页
 纭。将何所适从。最是退溪之说。与栗谷迥然不同。取舍最难矣。公意则谁从。余曰。不问退溪与栗谷。而同于朱子者从之。不同于朱子者不从而已。公曰。孰为同而孰为不同乎。余曰。格物二字。未见有不同者。而惟于物格二字。论议多岐矣。然朱子于章句。既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云。则是主物而言也无疑矣。至于或问则又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云。则其意视章句益明且详矣。退溪庚午以前论物格。则皆是知至而非物格也。庚午岁。与奇高峰书。大悟前见之非。而始主物而言则即同于朱子说矣。然虽同于朱子。而其主意实有不同者。朱子既曰。表里精粗无不到云。则是兼体用而言者也。退溪之说则舍体而只言用。此其不同之大者也。且朱子之所谓无不到。所谓诣其极者。盖谓物之理已尽。而更无可格之意也。今退溪之说则其曰发见。其曰显行。其曰非死物云者。皆以为理是活物。故自能运用。由此至彼也。此又与朱子之意不同者也。栗谷之言则与朱子吻合。而亦有发明朱子之馀蕴者。通透明白。虽粗解文理者。无不领会矣。公曰然矣。
纭。将何所适从。最是退溪之说。与栗谷迥然不同。取舍最难矣。公意则谁从。余曰。不问退溪与栗谷。而同于朱子者从之。不同于朱子者不从而已。公曰。孰为同而孰为不同乎。余曰。格物二字。未见有不同者。而惟于物格二字。论议多岐矣。然朱子于章句。既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云。则是主物而言也无疑矣。至于或问则又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云。则其意视章句益明且详矣。退溪庚午以前论物格。则皆是知至而非物格也。庚午岁。与奇高峰书。大悟前见之非。而始主物而言则即同于朱子说矣。然虽同于朱子。而其主意实有不同者。朱子既曰。表里精粗无不到云。则是兼体用而言者也。退溪之说则舍体而只言用。此其不同之大者也。且朱子之所谓无不到。所谓诣其极者。盖谓物之理已尽。而更无可格之意也。今退溪之说则其曰发见。其曰显行。其曰非死物云者。皆以为理是活物。故自能运用。由此至彼也。此又与朱子之意不同者也。栗谷之言则与朱子吻合。而亦有发明朱子之馀蕴者。通透明白。虽粗解文理者。无不领会矣。公曰然矣。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语录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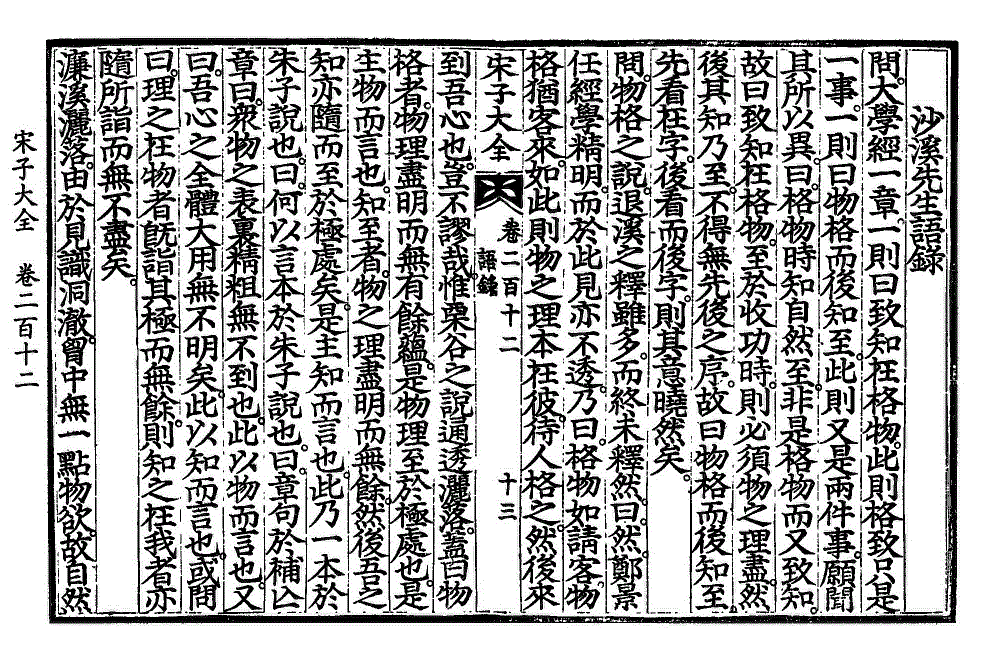 沙溪先生语录
沙溪先生语录问。大学经一章。一则曰致知在格物。此则格致只是一事。一则曰物格而后知至。此则又是两件事。愿闻其所以异。曰。格物时知自然至。非是格物而又致知。故曰致知在格物。至于收功时。则必须物之理尽。然后其知乃至。不得无先后之序。故曰物格而后知至。先看在字。后看而后字。则其意晓然矣。
问。物格之说。退溪之释虽多。而终未释然。曰。然。郑景任经学精明。而于此见亦不透。乃曰。格物如请客。物格犹客来。如此则物之理本在彼。待人格之。然后来到吾心也。岂不谬哉。惟栗谷之说通透洒落。盖曰物格者。物理尽明而无有馀蕴。是物理至于极处也。是生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尽明而无馀。然后吾之知亦随而至于极处矣。是主知而言也。此乃一本于朱子说也。曰。何以言本于朱子说也。曰。章句于补亡章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此以物而言也。又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以知而言也。或问曰。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馀。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
濂溪洒落。由于见识洞澈。胸中无一点物欲。故自然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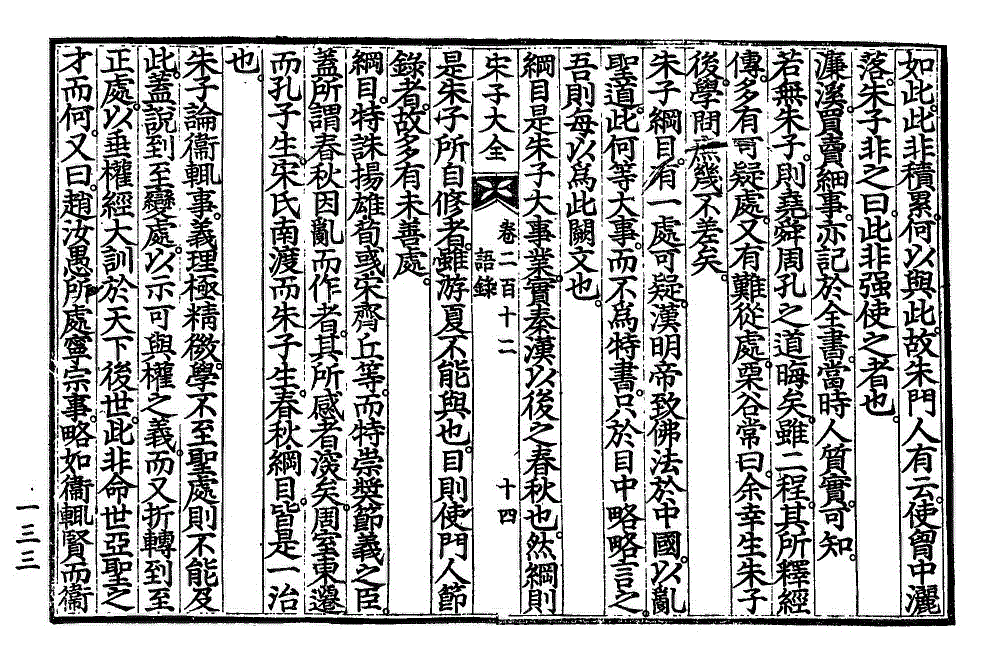 如此。此非积累。何以与此。故朱门人有云。使胸中洒落。朱子非之曰。此非强使之者也。
如此。此非积累。何以与此。故朱门人有云。使胸中洒落。朱子非之曰。此非强使之者也。濂溪。买卖细事。亦记于全书。当时人质实。可知。
若无朱子。则尧舜,周孔之道晦矣。虽二程。其所释经传。多有可疑处。又有难从处。栗谷常曰。余幸生朱子后。学问庶几不差矣。
朱子纲目。有一处可疑。汉明帝致佛法于中国。以乱圣道。此何等大事。而不为特书。只于目中略略言之。吾则每以为此阙文也。
纲目是朱子大事业。实秦汉以后之春秋也。然纲则是朱子所自修者。虽游夏不能与也。目则使门人节录者。故多有未善处。
纲目。特诛扬雄,荀彧,宋齐丘等。而特崇奖节义之臣。盖所谓春秋因乱而作者。其所感者深矣。周室东迁而孔子生。宋氏南渡而朱子生。春秋,纲目。皆是一治也。
朱子论卫辄事。义理极精微。学不至圣处则不能及此。盖说到至变处。以示可与权之义。而又折转到至正处。以垂权经大训于天下后世。此非命世亚圣之才而何。又曰。赵汝愚所处宁宗事。略如卫辄贤而卫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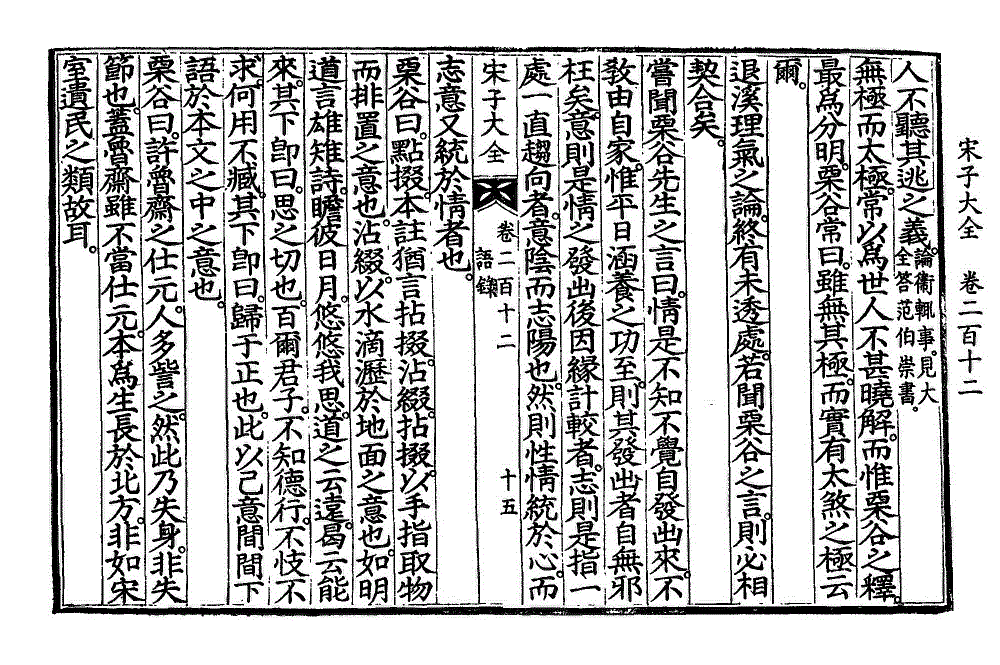 人不听其逃之义。(论卫辄事。见大全答范伯崇书。)
人不听其逃之义。(论卫辄事。见大全答范伯崇书。)无极而太极。常以为世人不甚晓解。而惟栗谷之释。最为分明。栗谷常曰。虽无其极。而实有太煞之极云尔。
退溪理气之论。终有未透处。若闻栗谷之言。则必相契合矣。
尝闻栗谷先生之言曰。情是不知不觉自发出来。不教由自家。惟平日涵养之功至。则其发出者自无邪枉矣。意则是情之发出后因缘计较者。志则是指一处一直趋向者。意阴而志阳也。然则性情统于心。而志意又统于情者也。
栗谷曰。点掇。本注犹言拈掇。沾缀。拈掇。以手指取物而排置之意也。沾缀。以水滴沥于地面之意也。如明道言雄雉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其下即曰。思之切也。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下即曰。归于正也。此以己意间间下语于本文之中之意也。
栗谷曰。许鲁斋之仕元。人多訾之。然此乃失身。非失节也。盖鲁斋虽不当仕元。本为生长于北方。非如宋室遗民之类故耳。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4L 页
 余尝与金清风权。同在栗谷门下。清风为请其祖金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清风怃然而退。私于余曰。欲请不许之由于先生。而严不敢焉。君须待间请问也。余如其说则答曰。其处死之义甚未安。故不许矣。余以是言于清风。后竟不敢复请云。
余尝与金清风权。同在栗谷门下。清风为请其祖金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清风怃然而退。私于余曰。欲请不许之由于先生。而严不敢焉。君须待间请问也。余如其说则答曰。其处死之义甚未安。故不许矣。余以是言于清风。后竟不敢复请云。尝问于栗谷曰。先生于事为。无所不通。将帅之任。亦可当否。栗谷曰。若自任将兵之事。则吾亦未敢自信。亦可为将帅之师矣。
尝问于栗谷曰。先生担当国事。如到极难处则将如何。栗谷曰。继之以死而已。学问亦然。成不成姑置不论。当鞠躬尽瘁。毙而后已可也。
尝问于栗谷曰。先生在枫岳时。未尝变形乎。栗谷笑曰。既已入山。虽不变形。何益于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须问也。
栗谷入山时。自号义庵。盖亦志乎集义生浩然气也。余尝从容谓宋龟峰丈席。不必干与时事以取祸害。龟峰不能用。栗谷秉铨时。龟峰列书若干人以荐。栗谷粘之窗间。余往见而大惊。请去之。栗谷曰。此何妨泛论人才。是伊川之所不辞也。
栗谷与人言。不间亲疏。必豁然无所碍阻。倾倒无馀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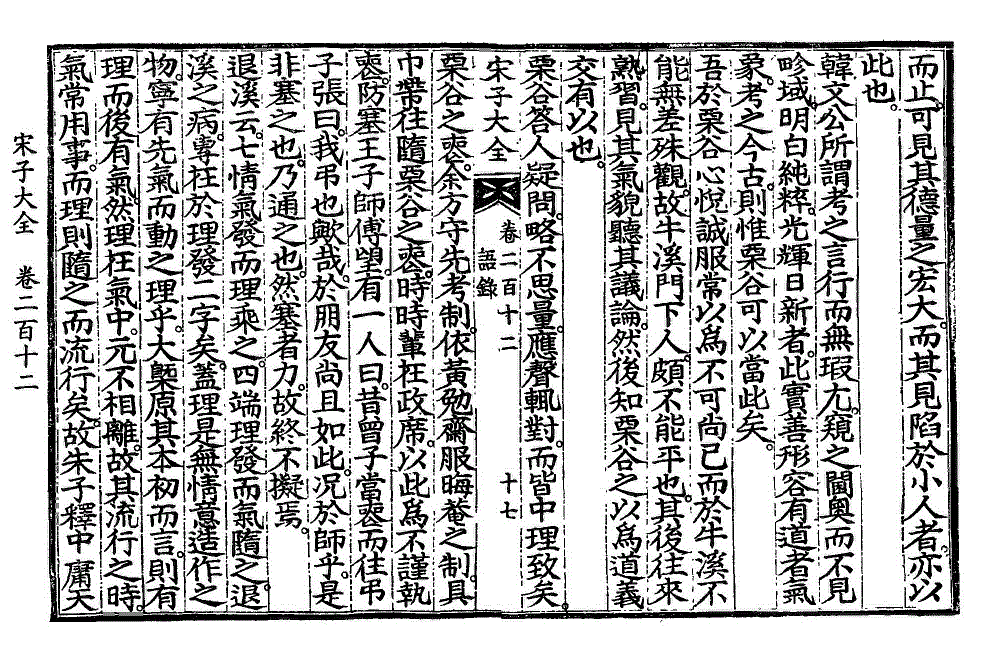 而止。可见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见陷于小人者。亦以此也。
而止。可见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见陷于小人者。亦以此也。韩文公所谓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纯粹。光辉日新者。此实善形容有道者气象。考之今古。则惟栗谷可以当此矣。
吾于栗谷心悦诚服常以为不可尚已而于牛溪不能无差殊观。故牛溪门下人。颇不能平也。其后往来熟习。见其气貌听其议论。然后知栗谷之以为道义交有以也。
栗谷答人疑问。略不思量。应声辄对。而皆中理致矣。栗谷之丧。余方守先考制。依黄勉斋服晦庵之制。具巾带往随栗谷之丧。时时辈在政席。以此为不谨执丧。防塞王子师傅望。有一人曰。昔曾子当丧而往吊子张曰。我吊也欤哉。于朋友尚且如此。况于师乎。是非塞之也。乃通之也。然塞者力。故终不拟焉。
退溪云。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四端理发而气随之。退溪之病。专在于理发二字矣。盖理是无情意造作之物。宁有先气而动之理乎。大槩原其本初而言。则有理而后有气。然理在气中。元不相离。故其流行之时。气常用事。而理则随之而流行矣。故朱子释中庸天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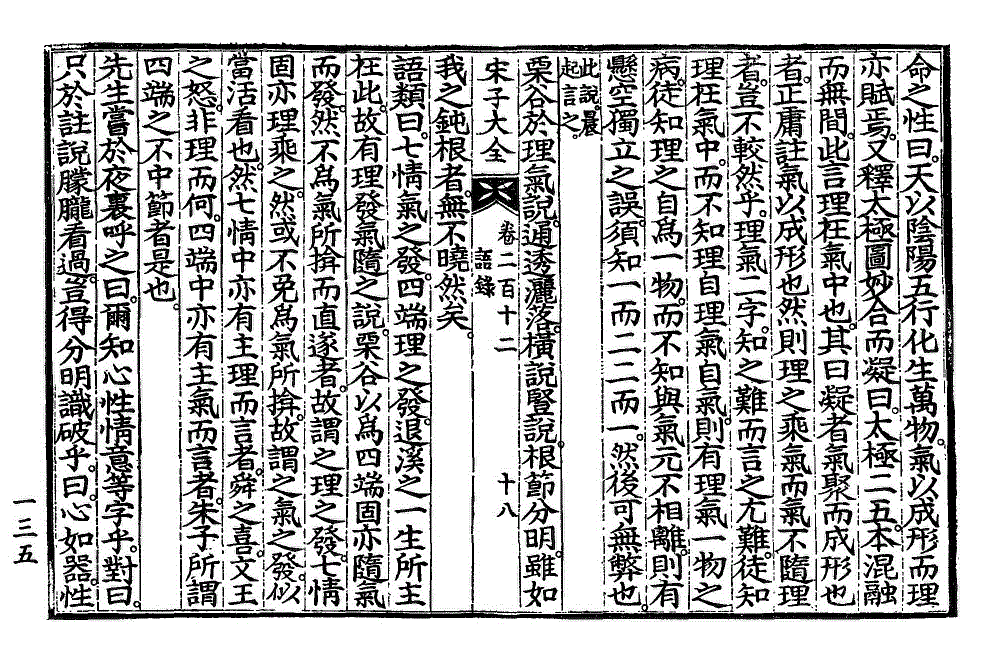 命之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又释太极图妙合而凝曰。太极二五。本混融而无间。此言理在气中也。其曰凝者气聚而成形也者。正庸注气以成形也。然则理之乘气而气不随理者。岂不较然乎。理气二字。知之难而言之尤难。徒知理在气中。而不知理自理气自气。则有理气一物之病。徒知理之自为一物。而不知与气元不相离。则有悬空独立之误。须知一而二二而一。然后可无弊也。(此说。晨起言之。)
命之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又释太极图妙合而凝曰。太极二五。本混融而无间。此言理在气中也。其曰凝者气聚而成形也者。正庸注气以成形也。然则理之乘气而气不随理者。岂不较然乎。理气二字。知之难而言之尤难。徒知理在气中。而不知理自理气自气。则有理气一物之病。徒知理之自为一物。而不知与气元不相离。则有悬空独立之误。须知一而二二而一。然后可无弊也。(此说。晨起言之。)栗谷于理气说。通透洒落。横说竖说。根节分明。虽如我之钝根者。无不晓然矣。
语类曰。七情气之发。四端理之发。退溪之一生所主在此。故有理发气随之说。栗谷以为四端固亦随气而发。然不为气所掩而直遂者。故谓之理之发。七情固亦理乘之。然或不免为气所掩。故谓之气之发。似当活看也。然七情中亦有主理而言者。舜之喜。文王之怒。非理而何。四端中亦有主气而言者。朱子所谓四端之不中节者是也。
先生尝于夜里呼之曰。尔知心性情意等字乎。对曰。只于注说朦胧看过。岂得分明识破乎。曰。心如器。性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6H 页
 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泻出者。贮此水而有时泻出者器也。函此性而发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别也。此情既发之后。经营谋画者意也。指向一事而欲之者志也。思与志相近。但志则大而思则小也。念虑则思之属。而虑有虞度之意矣。又曰。情是不知不觉闯然发出。不由自家者也。以此发出者。经营谋画者。意也。至此然后始由自家。故大学不曰诚情而。曰诚意也。
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泻出者。贮此水而有时泻出者器也。函此性而发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别也。此情既发之后。经营谋画者意也。指向一事而欲之者志也。思与志相近。但志则大而思则小也。念虑则思之属。而虑有虞度之意矣。又曰。情是不知不觉闯然发出。不由自家者也。以此发出者。经营谋画者。意也。至此然后始由自家。故大学不曰诚情而。曰诚意也。博文约礼二者。于圣门之学。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栗谷每诵此言以教之。然余所见。栗谷于博文之功最多。而于约礼犹有所未至也。
退溪集。中自言乐处甚多。昔明道诗。言傍人不识余心乐。朱子犹以为少时作。康节多言乐处。而其一曰。真乐攻心不奈何。朱子笑之以为非真乐。今退溪只以退居静处。随意看书。是非不到为乐。此诚乐矣。然于孔颜之乐则恐未能与也。孔颜之乐。周子,朱子皆引而不发。此岂易言者哉。
余之一生所受用者。司马公平生所为。无不可对人言者也。温公若无慎独之功。何以与此。此一句先生所雅言也。大学诚意章。中庸首章。旨诀昭如日星。而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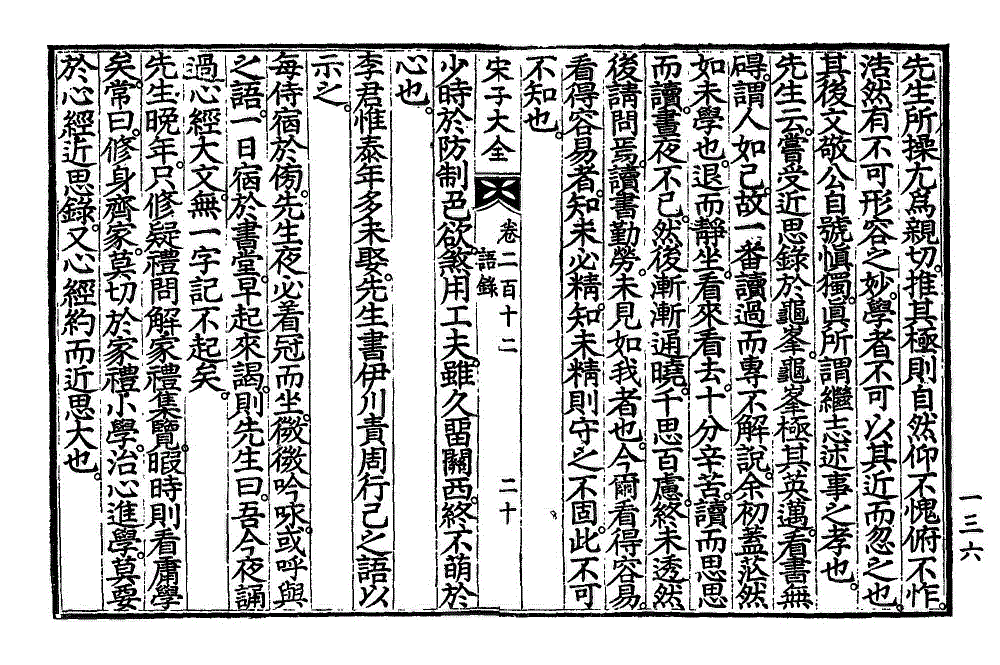 先生所操尤为亲切。推其极则自然仰不愧俯不怍。浩然有不可形容之妙。学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后文敬公自号慎独。真所谓继志述事之孝也。
先生所操尤为亲切。推其极则自然仰不愧俯不怍。浩然有不可形容之妙。学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后文敬公自号慎独。真所谓继志述事之孝也。先生云。尝受近思录于龟峰。龟峰极其英迈。看书无碍。谓人如己。故一番读过而专不解说。余初盖茫然如未学也。退而静坐。看来看去。十分辛苦。读而思思而读。昼夜不已。然后渐渐通晓。千思百虑。终未透然后请问焉。读书勤劳。未见如我者也。今尔看得容易。看得容易者。知未必精。知未精则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也。
少时于防制色欲。煞用工夫。虽久留关西。终不萌于心也。
李君惟泰年多未娶。先生书伊川责周行己之语以示之。
每侍宿于傍。先生夜必着冠而坐。微微吟咏。或呼与之语。一日宿于书堂。早起来谒。则先生曰。吾今夜诵过心经大文。无一字记不起矣。
先生晚年。只修疑礼问解,家礼集览。暇时则看庸学矣。常曰。修身齐家。莫切于家礼,小学。治心进学。莫要于心经,近思录。又心经约而近思大也。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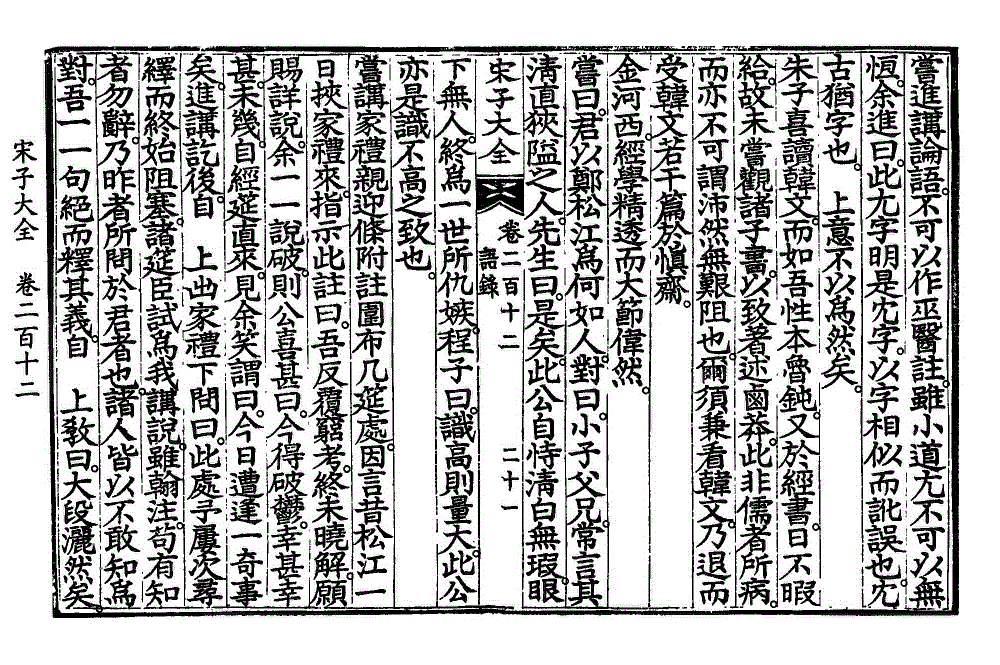 尝进讲论语。不可以作巫医注。虽小道尤不可以无恒。余进曰。此尤字明是冘字。以字相似而讹误也。冘古犹字也。 上意不以为然矣。
尝进讲论语。不可以作巫医注。虽小道尤不可以无恒。余进曰。此尤字明是冘字。以字相似而讹误也。冘古犹字也。 上意不以为然矣。朱子喜读韩文。而如吾性本鲁钝。又于经书。日不暇给。故未尝观诸子书。以致著述卤莽。此非儒者所病。而亦不可谓沛然无艰阻也。尔须兼看韩文。乃退而受韩文若干篇于慎斋。
金河西。经学精透而大节伟然。
尝曰。君以郑松江为何如人。对曰。小子父兄。常言其清直狭隘之人。先生曰。是矣。此公自恃清白无瑕。眼下无人。终为一世所仇嫉。程子曰。识高则量大。此公亦是识不高之致也。
尝讲家礼亲迎条附注围布几筵处。因言昔松江一日挟家礼来。指示此注曰。吾反覆穷考。终未晓解。愿赐详说。余一一说破。则公喜甚曰。今得破郁。幸甚幸甚。未几。自经筵直来。见余笑谓曰。今日遭逢一奇事矣。进讲讫后。自 上出家礼下问曰。此处予屡次寻绎而终始阻塞。诸筵臣试为我讲说。虽翰注。苟有知者勿辞。乃昨者所问于君者也。诸人皆以不敢知为对。吾一一句绝而释其义。自 上教曰。大段洒然矣。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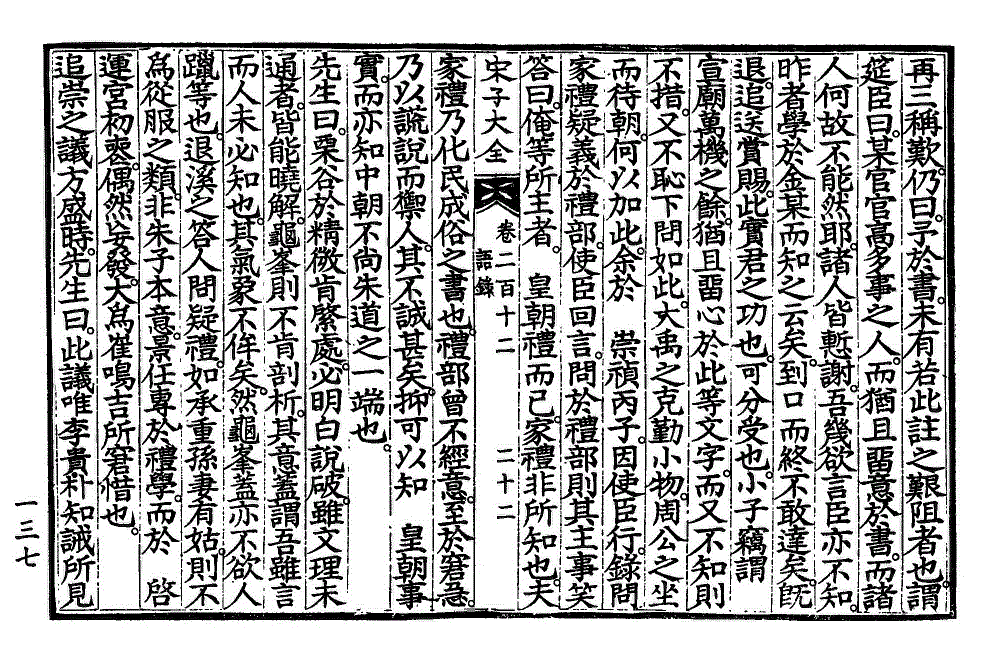 再三称叹。仍曰。予于书。未有若此注之艰阻者也。谓筵臣曰。某官官高多事之人。而犹且留意于书。而诸人何故不能然耶。诸人皆惭谢。吾几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学于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终不敢达矣。既退。追送赏赐。此实君之功也。可分受也。小子窃谓 宣庙万机之馀。犹且留心于此等文字。而又不知则不措。又不耻下问如此。大禹之克勤小物。周公之坐而待朝。何以加此。余于 崇祯丙子。因使臣行。录问家礼疑义于礼部。使臣回言。问于礼部则其主事笑答曰。俺等所主者。 皇朝礼而已。家礼非所知也。夫家礼乃化民成俗之书也。礼部曾不经意。至于窘急。乃以谎说而御人。其不诚甚矣。抑可以知 皇朝事实。而亦知中朝不尚朱道之一端也。
再三称叹。仍曰。予于书。未有若此注之艰阻者也。谓筵臣曰。某官官高多事之人。而犹且留意于书。而诸人何故不能然耶。诸人皆惭谢。吾几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学于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终不敢达矣。既退。追送赏赐。此实君之功也。可分受也。小子窃谓 宣庙万机之馀。犹且留心于此等文字。而又不知则不措。又不耻下问如此。大禹之克勤小物。周公之坐而待朝。何以加此。余于 崇祯丙子。因使臣行。录问家礼疑义于礼部。使臣回言。问于礼部则其主事笑答曰。俺等所主者。 皇朝礼而已。家礼非所知也。夫家礼乃化民成俗之书也。礼部曾不经意。至于窘急。乃以谎说而御人。其不诚甚矣。抑可以知 皇朝事实。而亦知中朝不尚朱道之一端也。先生曰。栗谷于精微肯綮处。必明白说破。虽文理未通者。皆能晓解。龟峰则不肯剖析。其意盖谓吾虽言而人未必知也。其气象不侔矣。然龟峰盖亦不欲人躐等也。退溪之答人问疑礼。如承重孙妻有姑。则不为从服之类。非朱子本意。景任专于礼学。而于 启运宫初丧。偶然妄发。大为崔鸣吉所窘惜也。
追崇之议方盛时。先生曰。此议唯李贵,朴知诫所见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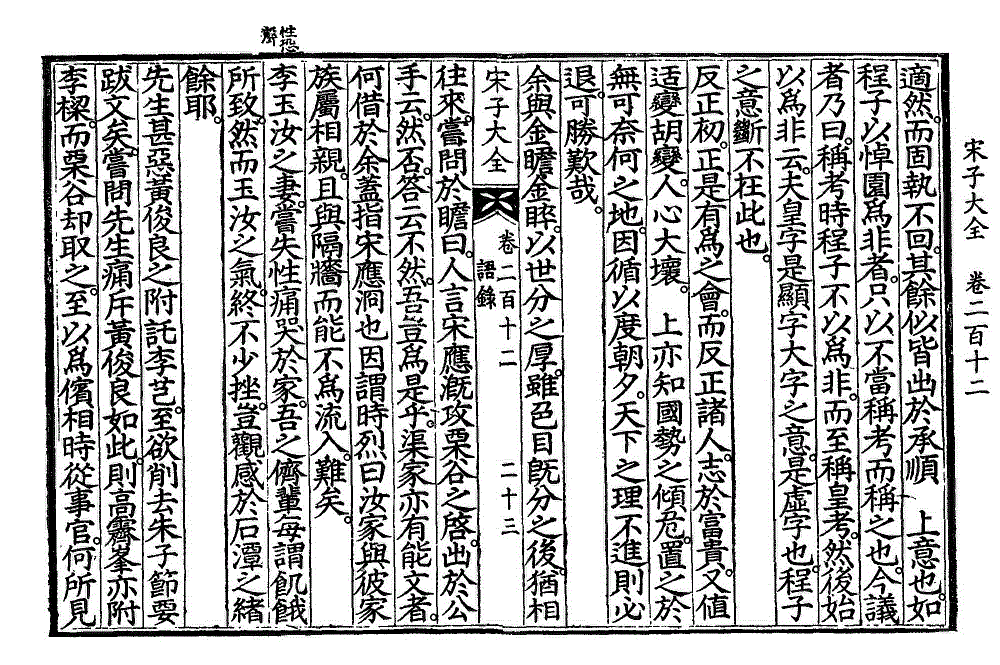 适然。而固执不回。其馀似皆出于承顺 上意也。如程子以悼园为非者。只以不当称考而称之也。今议者乃曰。称考时程子不以为非。而至称皇考。然后始以为非云。夫皇字是显字大字之意。是虚字也。程子之意断不在此也。
适然。而固执不回。其馀似皆出于承顺 上意也。如程子以悼园为非者。只以不当称考而称之也。今议者乃曰。称考时程子不以为非。而至称皇考。然后始以为非云。夫皇字是显字大字之意。是虚字也。程子之意断不在此也。反正初。正是有为之会。而反正诸人。志于富贵。又值适变胡变。人心大坏。 上亦知国势之倾危。置之于无可奈何之地。因循以度朝夕。天下之理不进则必退。可胜叹哉。
余与金瞻,金睟。以世分之厚。虽色目既分之后。犹相往来。尝问于瞻曰。人言宋应溉攻栗谷之启。出于公手云。然否。答云不然。吾岂为是乎。渠家亦有能文者。何借于余。盖指宋应浻也。因谓时烈曰。汝家与彼家族属相亲。且与隔墙而能不为流入。难矣。
李玉汝之妻。尝失性(性恐声)痛哭于家。吾之侪辈每谓饥饿所致。然而玉汝之气。终不少挫。岂观感于石潭之绪馀耶。
先生甚恶黄俊良之附托李芑。至欲削去朱子节要跋文矣。尝问先生痛斥黄俊良如此。则高霁峰亦附李梁。而栗谷却取之。至以为傧相时从事官。何所见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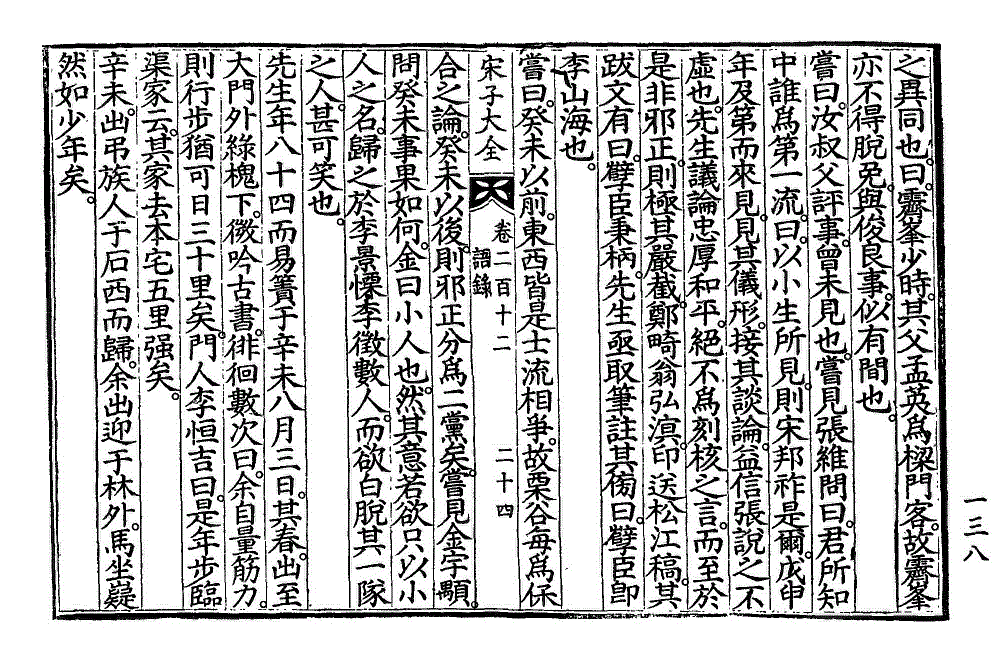 之异同也。曰。霁峰少时。其父孟英为梁门客。故霁峰亦不得脱免。与俊良事。似有间也。
之异同也。曰。霁峰少时。其父孟英为梁门客。故霁峰亦不得脱免。与俊良事。似有间也。尝曰。汝叔父评事。曾未见也。尝见张维问曰。君所知中谁为第一流。曰。以小生所见。则宋邦祚是尔。戊申年及第而来见。见其仪形。接其谈论。益信张说之不虚也。先生议论忠厚和平。绝不为刻核之言。而至于是非邪正。则极其严截。郑畸翁弘溟。印送松江稿。其跋文有曰。孽臣秉柄。先生亟取笔注其傍曰。孽臣即李山海也。
尝曰。癸未以前。东西皆是士流相争。故栗谷每为保合之论。癸未以后。则邪正分为二党矣。尝见金宇颙。问癸未事果如何。金曰小人也。然其意若欲只以小人之名。归之于李景慄,李徵数人。而欲白脱其一队之人。甚可笑也。
先生年八十四而易箦于辛未八月三日。其春。出至大门外绿槐下。微吟古书。徘徊数次曰。余自量筋力。则行步犹可日三十里矣。门人李恒吉曰。是年步临渠家云。其家去本宅五里强矣。
辛未。出吊族人于石西而归。余出迎于林外。马坐嶷然如少年矣。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9H 页
 慎独斋先生语录
慎独斋先生语录先生常衣上服著笠。一日以常服毛冠。步出于川上。余追至则曰。老亲无馔。欲令儿子求鱼矣。时季子益炼。持小网及钓竿在傍矣。
先生与庶弟同侍老先生。庶弟答尹参奉材书。称尊兄。先生止之曰。世俗不如是亟改之。庶弟未即从。先生以温言反覆谕之。改而后乃已。老先生但微哂而已。
先生定省老先生。虽已寝亦拜。老先生曰。父兄卧则不拜也。先生终不变。
辛卯进见。先生曰。平生以君为不甚虚疏。己丑以后。知君有客气。泰之则尤甚。此后有 召命。只可谢恩而已。吾则老矣。谢恩亦不可为矣。如此时节。以君辈之才。宁有可为之事。
人家以诅咒灭亡者。比比有之。君与明甫为邪不胜正之论。此甚酸论也。
有忠孝之实。则岂徒有学文之名而无其实者之比哉。(论李正宋太仆享事而云耳)
尝禀迁葬后虞祭。答曰。朱子只是设奠而已。丘氏变朱子说而为一虞。今君合而一之。君之讲礼。如是不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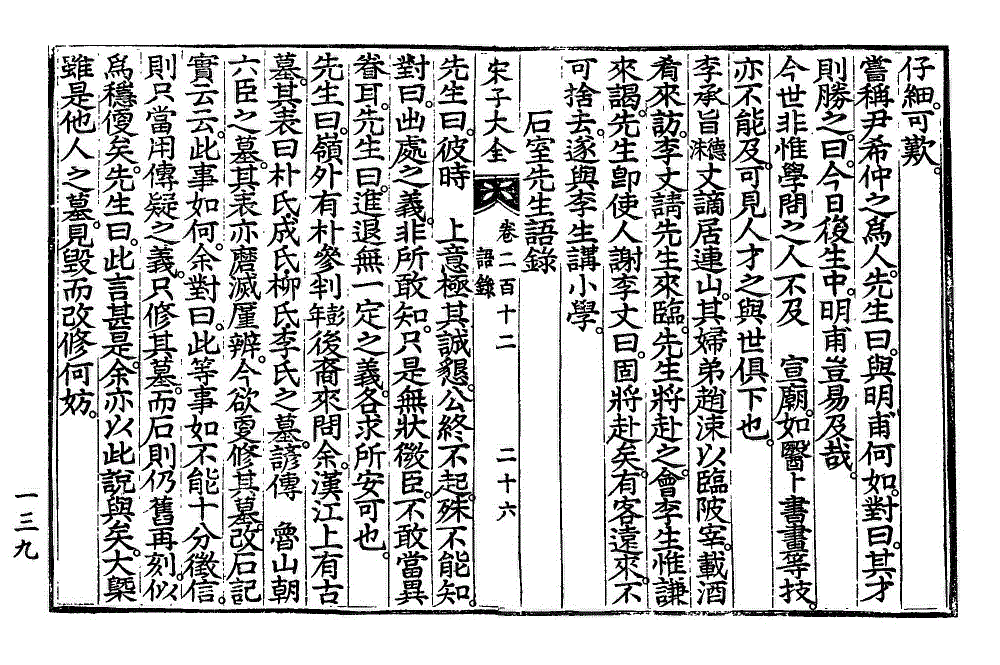 仔细。可叹。
仔细。可叹。尝称尹希仲之为人。先生曰。与明甫何如。对曰。其才则胜之。曰。今日后生中。明甫岂易及哉。
今世非惟学问之人不及 宣庙。如医卜书画等技。亦不能及。可见人才之与世俱下也。
李承旨(德洙)丈谪居连山。其妇弟赵涑以临陂宰。载酒肴来访。李丈请先生来临。先生将赴之。会李生惟谦来谒。先生即使人谢李丈曰。固将赴矣。有客远来。不可舍去。遂与李生讲小学。
石室先生语录
先生曰。彼时 上意极其诚恳。公终不起。殊不能知。对曰。出处之义。非所敢知。只是无状微臣。不敢当异眷耳。先生曰。进退无一定之义。各求所安可也。
先生曰。岭外有朴参判(彭年)后裔来问余。汉江上有古墓。其表曰朴氏,成氏,柳氏,李氏之墓。谚传 鲁山朝六臣之墓。其表亦磨灭廑辨。今欲更修其墓。改石记实云云。此事如何。余对曰。此等事如不能十分徵信。则只当用传疑之义。只修其墓。而石则仍旧再刻。似为稳便矣。先生曰。此言甚是。余亦以此说与矣。大槩虽是他人之墓。见毁而改修何妨。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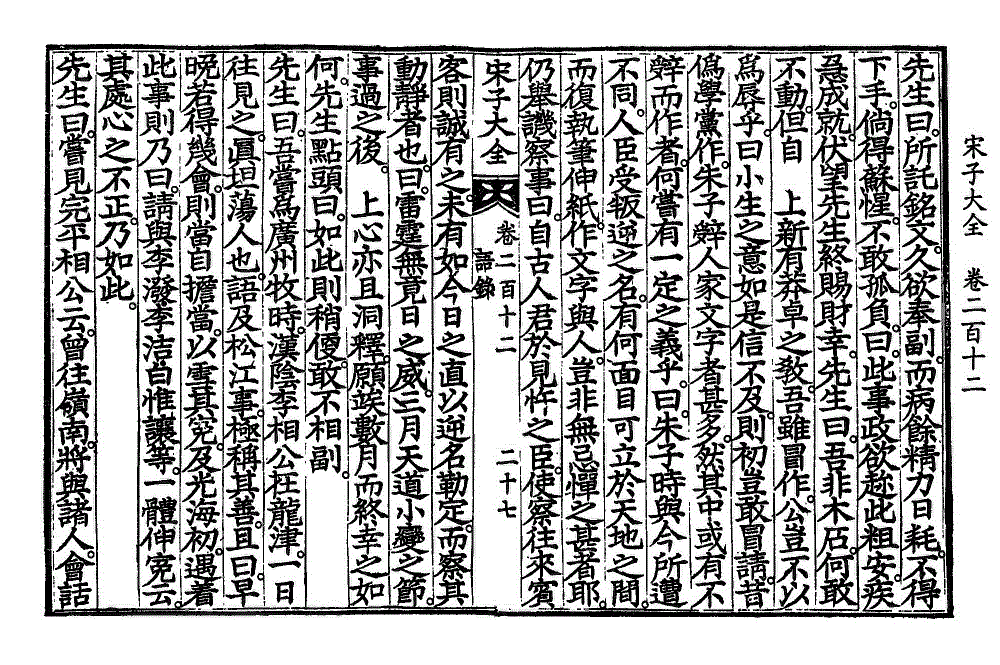 先生曰。所托铭文。久欲奉副。而病馀精力日耗。不得下手。倘得苏惺。不敢孤负。曰。此事政欲趁此粗安。疾急成就。伏望先生终赐财幸。先生曰。吾非木石。何敢不动。但自 上新有莽卓之教。吾虽冒作。公岂不以为辱乎。曰小生之意如是信不及。则初岂敢冒请。昔伪学党作。朱子辞人家文字者甚多。然其中或有不辞而作者。何尝有一定之义乎。曰。朱子时与今所遭不同。人臣受叛逆之名。有何面目可立于天地之间。而复执笔伸纸。作文字与人。岂非无忌惮之甚者耶。仍举讥察事曰。自古人君于见忤之臣。使察往来宾客则诚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直以逆名勒定。而察其动静者也。曰。雷霆无竟日之威。三月天道小变之节。事过之后。 上心亦且洞释。愿俟数月而终幸之如何。先生点头曰。如此则稍便。敢不相副。
先生曰。所托铭文。久欲奉副。而病馀精力日耗。不得下手。倘得苏惺。不敢孤负。曰。此事政欲趁此粗安。疾急成就。伏望先生终赐财幸。先生曰。吾非木石。何敢不动。但自 上新有莽卓之教。吾虽冒作。公岂不以为辱乎。曰小生之意如是信不及。则初岂敢冒请。昔伪学党作。朱子辞人家文字者甚多。然其中或有不辞而作者。何尝有一定之义乎。曰。朱子时与今所遭不同。人臣受叛逆之名。有何面目可立于天地之间。而复执笔伸纸。作文字与人。岂非无忌惮之甚者耶。仍举讥察事曰。自古人君于见忤之臣。使察往来宾客则诚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直以逆名勒定。而察其动静者也。曰。雷霆无竟日之威。三月天道小变之节。事过之后。 上心亦且洞释。愿俟数月而终幸之如何。先生点头曰。如此则稍便。敢不相副。先生曰。吾尝为广州牧时。汉阴李相公在龙津。一日往见之。真坦荡人也。语及松江事。极称其善。且曰。早晚若得几会。则当自担当。以雪其冤。及光海初。遇着此事则乃曰。请与李泼,李洁,白惟让等。一体伸冤云。其处心之不正。乃如此。
先生曰。尝见完平相公云。曾往岭南。将与诸人。会话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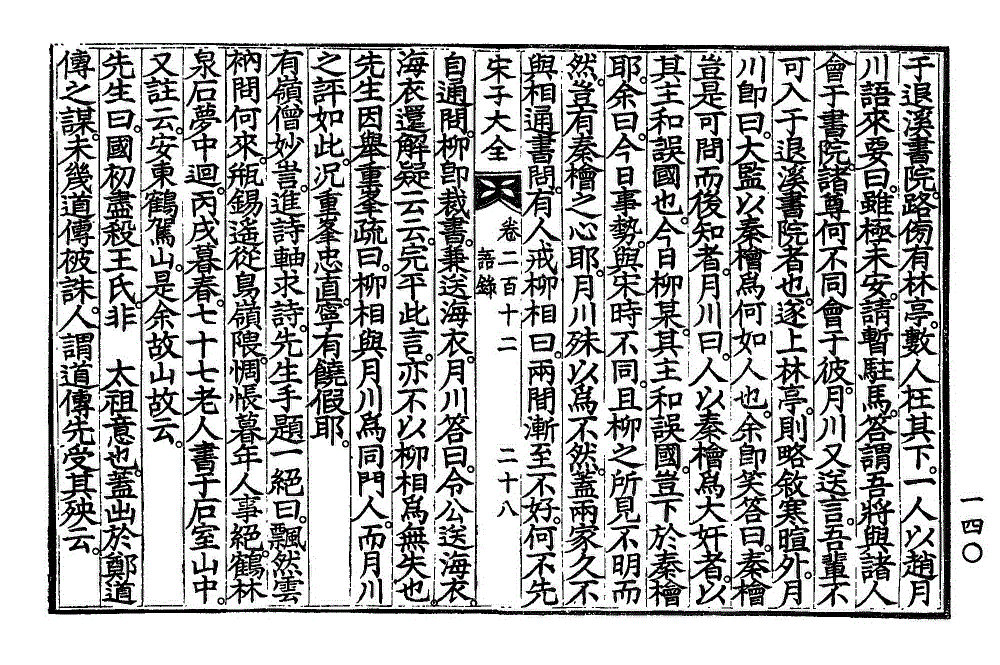 于退溪书院。路傍有林亭。数人在其下。一人以赵月川语来要曰。虽极未安。请暂驻马。答谓吾将与诸人会于书院。诸尊何不同会于彼。月川又送言。吾辈不可入于退溪书院者也。遂上林亭。则略叙寒暄外。月川即曰。大监以秦桧为何如人也。余即笑答曰。秦桧岂是可问而后知者。月川曰。人以秦桧为大奸者。以其主和误国也。今日柳某。其主和误国。岂下于秦桧耶。余曰。今日事势。与宋时不同。且柳之所见不明而然。岂有秦桧之心耶。月川殊以为不然。盖两家久不与相通书问。有人戒柳相曰。两间渐至不好。何不先自通问。柳即裁书。兼送海衣。月川答曰。令公送海衣。海衣还解疑云云。完平此言。亦不以柳相为无失也。先生因举重峰疏曰。柳相与月川为同门人。而月川之评如此。况重峰忠直。宁有饶假耶。
于退溪书院。路傍有林亭。数人在其下。一人以赵月川语来要曰。虽极未安。请暂驻马。答谓吾将与诸人会于书院。诸尊何不同会于彼。月川又送言。吾辈不可入于退溪书院者也。遂上林亭。则略叙寒暄外。月川即曰。大监以秦桧为何如人也。余即笑答曰。秦桧岂是可问而后知者。月川曰。人以秦桧为大奸者。以其主和误国也。今日柳某。其主和误国。岂下于秦桧耶。余曰。今日事势。与宋时不同。且柳之所见不明而然。岂有秦桧之心耶。月川殊以为不然。盖两家久不与相通书问。有人戒柳相曰。两间渐至不好。何不先自通问。柳即裁书。兼送海衣。月川答曰。令公送海衣。海衣还解疑云云。完平此言。亦不以柳相为无失也。先生因举重峰疏曰。柳相与月川为同门人。而月川之评如此。况重峰忠直。宁有饶假耶。有岭僧妙訔。进诗轴求诗。先生手题一绝曰。飘然云衲问何来。瓶锡遥从鸟岭隈。惆怅暮年人事绝。鹤林泉石梦中回。丙戌暮春。七十七老人书于石室山中。又注云。安东鹤驾山。是余故山故云。
先生曰。国初尽杀王氏。非 太祖意也。盖出于郑道传之谋。未几道传被诛。人谓道传先受其殃云。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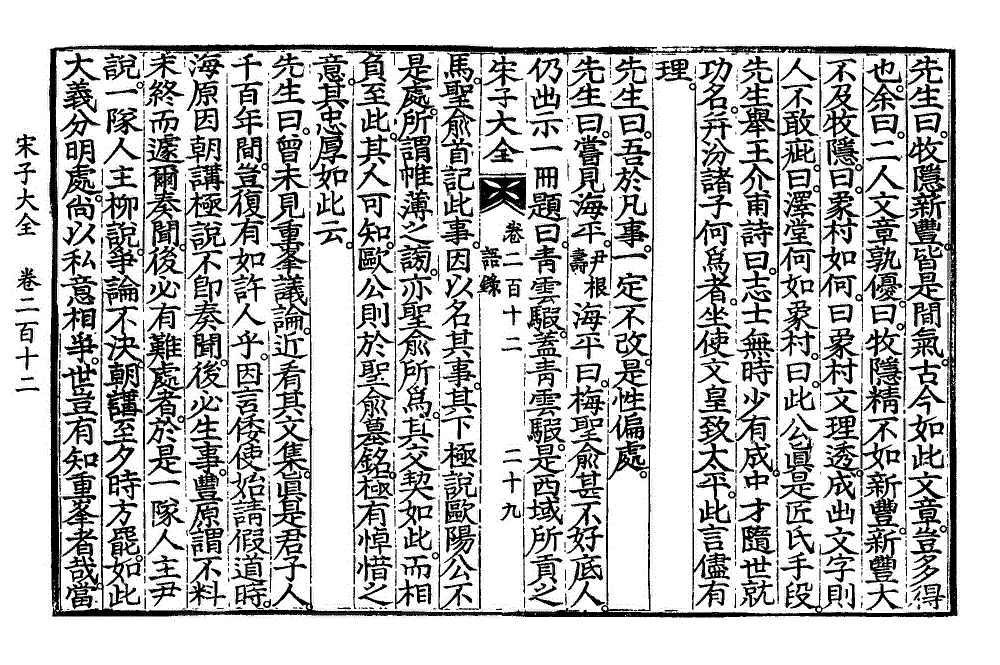 先生曰。牧隐,新丰。皆是间气。古今如此文章。岂多得也。余曰。二人文章孰优。曰。牧隐精不如新丰。新丰大不及牧隐。曰。象村如何。曰象村文理透。成出文字则人不敢疵。曰。泽堂何如象村。曰。此公真是匠氏手段。先生举王介甫诗曰。志士无时少有成。中才随世就功名。并汾诸子何为者。坐使文皇致太平。此言尽有理。
先生曰。牧隐,新丰。皆是间气。古今如此文章。岂多得也。余曰。二人文章孰优。曰。牧隐精不如新丰。新丰大不及牧隐。曰。象村如何。曰象村文理透。成出文字则人不敢疵。曰。泽堂何如象村。曰。此公真是匠氏手段。先生举王介甫诗曰。志士无时少有成。中才随世就功名。并汾诸子何为者。坐使文皇致太平。此言尽有理。先生曰。吾于凡事。一定不改。是性偏处。
先生曰。尝见海平。(尹根寿)海平曰。梅圣俞甚不好底人。仍出示一册题曰。青云騢。盖青云騢。是西域所贡之马。圣俞首记此事。因以名其事。其下极说欧阳公不是处。所谓帷薄之谤。亦圣俞所为。其交契如此。而相负至此。其人可知。欧公则于圣俞墓铭。极有悼惜之意。其忠厚如此云。
先生曰。曾未见重峰议论。近看其文集。真是君子人。千百年间。岂复有如许人乎。因言倭使始请假道时。海原因朝讲极说不即奏闻。后必生事。丰原谓不料未终而遽尔奏闻。后必有难处者。于是一队人主尹说。一队人主柳说。争论不决。朝讲至夕时方罢。如此大义分明处。尚以私意相争。世岂有知重峰者哉。当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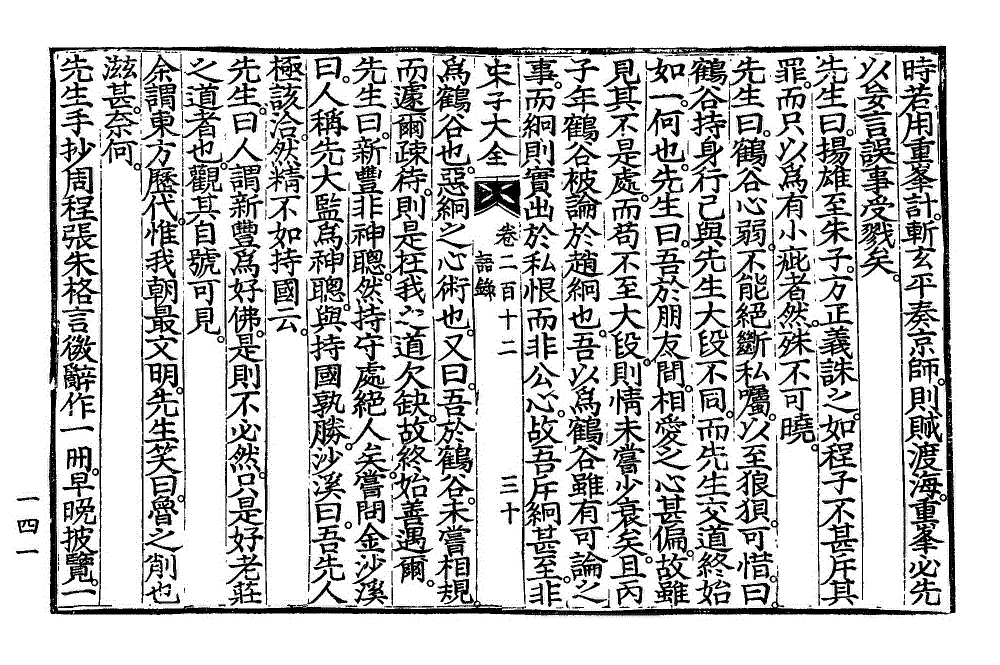 时若用重峰计。斩玄平奏京师。则贼渡海。重峰必先以妄言误事受戮矣。
时若用重峰计。斩玄平奏京师。则贼渡海。重峰必先以妄言误事受戮矣。先生曰。扬雄至朱子。方正义诛之。如程子不甚斥其罪。而只以为有小疵者然。殊不可晓。
先生曰。鹤谷心弱。不能绝断私嘱。以至狼狈。可惜。曰。鹤谷持身行己与先生大段不同。而先生交道终始如一。何也。先生曰。吾于朋友间。相爱之心甚偏。故虽见其不是处。而苟不至大段。则情未尝少衰矣。且丙子年鹤谷被论于赵絅也。吾以为鹤谷虽有可论之事。而絅则实出于私恨而非公心。故吾斥絅甚至。非为鹤谷也。恶絅之心术也。又曰。吾于鹤谷。未尝相规。而遽尔疏待。则是在我之道欠缺。故终始善遇尔。
先生曰。新丰非神聪。然持守处绝人矣。尝问金沙溪曰。人称先大监为神聪。与持国孰胜。沙溪曰。吾先人极该洽。然精不如持国云。
先生曰。人谓新丰为好佛。是则不必然。只是好老庄之道者也。观其自号可见。
余谓东方历代。惟我朝最文明。先生笑曰。鲁之削也滋甚。奈何。
先生手抄周程张朱格言微辞作一册。早晚披览。一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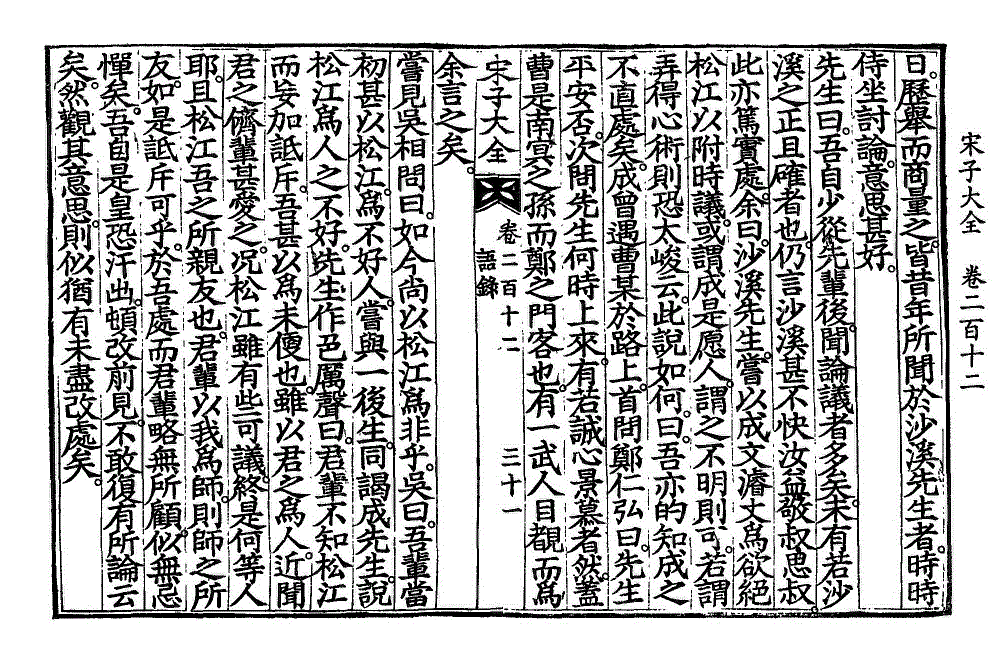 日。历举而商量之。皆昔年所闻于沙溪先生者。时时侍坐讨论。意思甚好。
日。历举而商量之。皆昔年所闻于沙溪先生者。时时侍坐讨论。意思甚好。先生曰。吾自少从先辈后。闻论议者多矣。未有若沙溪之正且确者也。仍言沙溪甚不快汝益,敬叔,思叔。此亦笃实处。余曰。沙溪先生。尝以成文浚丈为欲绝松江以附时议。或谓成是愿人。谓之不明则可。若谓弄得心术则恐太峻云。此说如何。曰。吾亦的知成之不直处矣。成曾遇曹某于路上。首问郑仁弘曰。先生平安否。次问先生何时上来。有若诚心景慕者然。盖曹是南冥之孙而郑之门客也。有一武人目睹而为余言之矣。
尝见吴相问曰。如今尚以松江为非乎。吴曰。吾辈当初甚以松江。为不好人。尝与一后生。同谒成先生。说松江为人之不好。先生作色厉声曰。君辈不知松江而妄加诋斥。吾甚以为未便也。虽以君之为人。近闻君之侪辈甚爱之。况松江虽有些可议。终是何等人耶。且松江吾之所亲友也。君辈以我为师。则师之所友。如是诋斥可乎。于吾处而君辈略无所顾。似无忌惮矣。吾自是皇恐汗出。顿改前见。不敢复有所论云矣。然观其意思。则似犹有未尽改处矣。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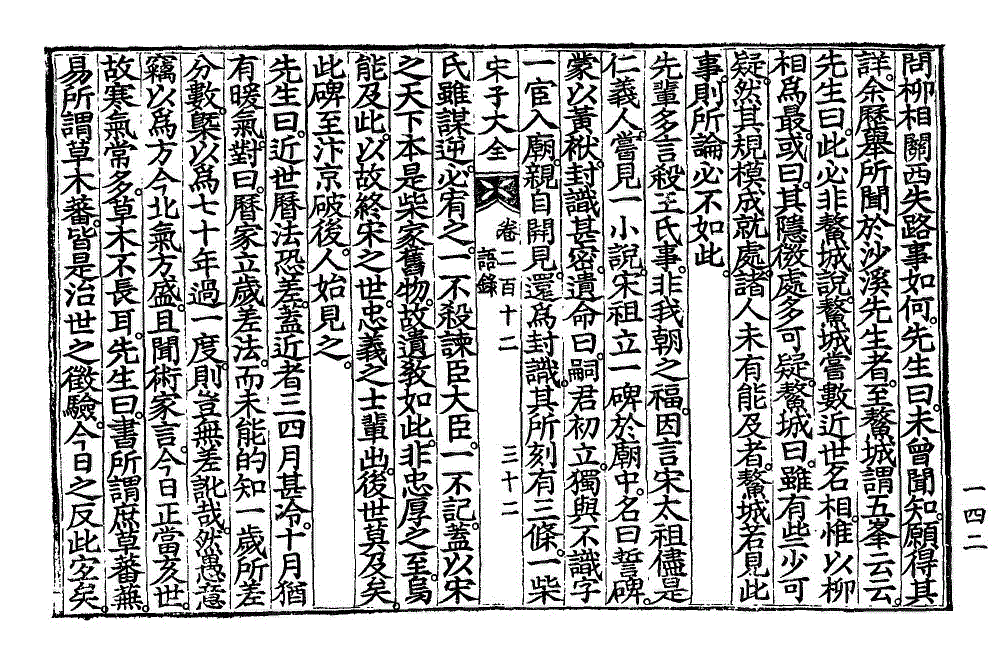 问柳相关西失路事如何。先生曰。未曾闻知。愿得其详。余历举所闻于沙溪先生者。至鳌城谓五峰云云。先生曰。此必非鳌城说。鳌城尝数近世名相。惟以柳相为最。或曰。其隐微处多可疑。鳌城曰。虽有些少可疑。然其规模成就处。诸人未有能及者。鳌城若见此事。则所论必不如此。
问柳相关西失路事如何。先生曰。未曾闻知。愿得其详。余历举所闻于沙溪先生者。至鳌城谓五峰云云。先生曰。此必非鳌城说。鳌城尝数近世名相。惟以柳相为最。或曰。其隐微处多可疑。鳌城曰。虽有些少可疑。然其规模成就处。诸人未有能及者。鳌城若见此事。则所论必不如此。先辈多言杀王氏事。非我朝之福。因言宋太祖尽是仁义人。尝见一小说。宋祖立一碑于庙中。名曰誓碑。蒙以黄袱。封识甚密。遗命曰。嗣君初立。独与不识字一宦入庙。亲自开见。还为封识。其所刻有三条。一柴氏虽谋逆。必宥之。一不杀谏臣大臣。一不记。盖以宋之天下本是柴家旧物。故遗教如此。非忠厚之至。乌能及此。以故终宋之世。忠义之士辈出。后世莫及矣。此碑至汴京破后。人始见之。
先生曰。近世历法恐差。盖近者三四月甚冷。十月犹有暖气。对曰。历家立岁差法。而未能的知一岁所差分数。槩以为七十年过一度。则岂无差讹哉。然愚意窃以为方今北气方盛。且闻术家言。今日正当亥世。故寒气常多。草木不长耳。先生曰。书所谓庶草蕃芜。易所谓草木蕃。皆是治世之徵验。今日之反此宜矣。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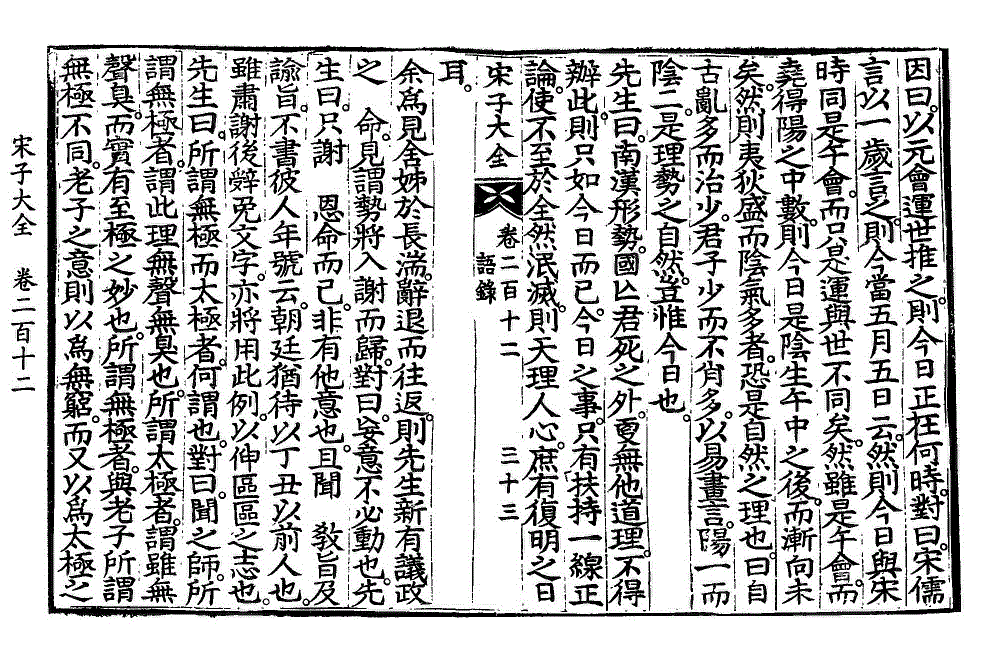 因曰。以元会运世推之。则今日正在何时。对曰。宋儒言以一岁言之。则今当五月五日云。然则今日与宋时同是午会。而只是运与世不同矣。然虽是午会。而尧得阳之中数。则今日是阴生午中之后。而渐向未矣。然则夷狄盛而阴气多者。恐是自然之理也。曰自古乱多而治少。君子少而不肖多。以易画言。阳一而阴二。是理势之自然。岂惟今日也。
因曰。以元会运世推之。则今日正在何时。对曰。宋儒言以一岁言之。则今当五月五日云。然则今日与宋时同是午会。而只是运与世不同矣。然虽是午会。而尧得阳之中数。则今日是阴生午中之后。而渐向未矣。然则夷狄盛而阴气多者。恐是自然之理也。曰自古乱多而治少。君子少而不肖多。以易画言。阳一而阴二。是理势之自然。岂惟今日也。先生曰。南汉形势。国亡君死之外。更无他道理。不得办此。则只如今日而已。今日之事。只有扶持一线正论。使不至于全然泯灭。则天理人心。庶有复明之日耳。
余为见舍姊于长湍。辞退而往返。则先生新有议政之 命。见谓势将入谢而归。对曰。妄意不必动也。先生曰。只谢 恩命而已。非有他意也。且闻 教旨及谕旨。不书彼人年号云。朝廷犹待以丁丑以前人也。虽肃谢后辞免文字。亦将用此例。以伸区区之志也。先生曰。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何谓也。对曰。闻之师。所谓无极者。谓此理无声无臭也。所谓太极者。谓虽无声臭。而实有至极之妙也。所谓无极者。与老子所谓无极不同。老子之意则以为无穷。而又以为太极之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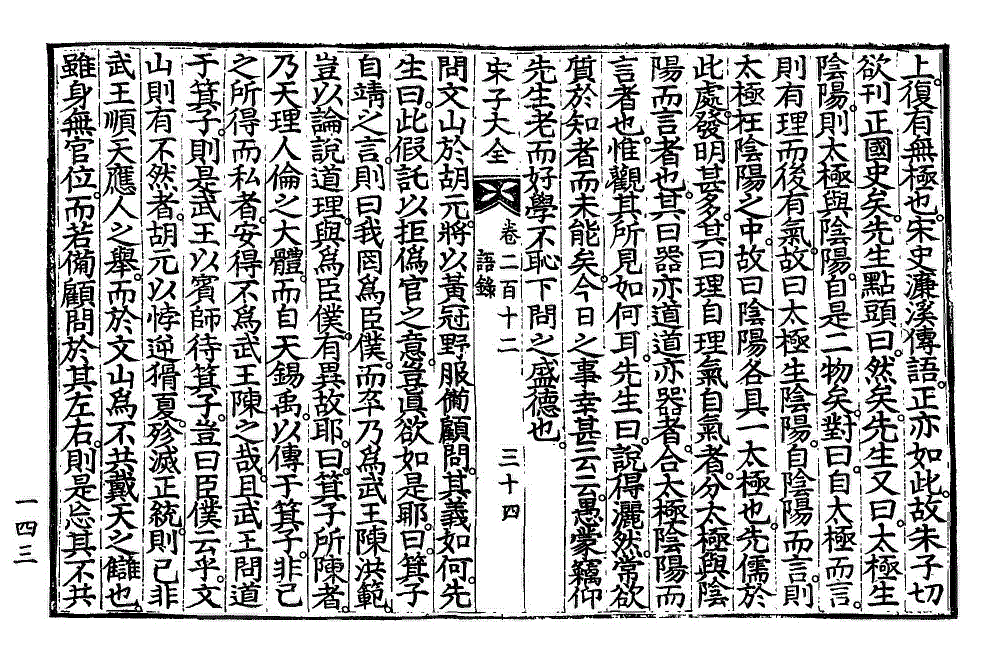 上。复有无极也。宋史濂溪传语。正亦如此。故朱子切欲刊正国史矣。先生点头曰。然矣。先生又曰。太极生阴阳。则太极与阴阳。自是二物矣。对曰。自太极而言。则有理而后有气。故曰太极生阴阳。自阴阳而言。则太极在阴阳之中。故曰阴阳各具一太极也。先儒于此处。发明甚多。其曰理自理气自气者。分太极与阴阳而言者也。其曰器亦道道亦器者。合太极阴阳而言者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先生曰。说得洒然。常欲质于知者而未能矣。今日之事幸甚云云。愚蒙窃仰先生老而好学不耻下问之盛德也。
上。复有无极也。宋史濂溪传语。正亦如此。故朱子切欲刊正国史矣。先生点头曰。然矣。先生又曰。太极生阴阳。则太极与阴阳。自是二物矣。对曰。自太极而言。则有理而后有气。故曰太极生阴阳。自阴阳而言。则太极在阴阳之中。故曰阴阳各具一太极也。先儒于此处。发明甚多。其曰理自理气自气者。分太极与阴阳而言者也。其曰器亦道道亦器者。合太极阴阳而言者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先生曰。说得洒然。常欲质于知者而未能矣。今日之事幸甚云云。愚蒙窃仰先生老而好学不耻下问之盛德也。问文山于胡元。将以黄冠野服备顾问。其义如何。先生曰。此假托以拒伪官之意。岂真欲如是耶。曰。箕子自靖之言。则曰我罔为臣仆。而卒乃为武王陈洪范。岂以论说道理。与为臣仆。有异故耶。曰。箕子所陈者。乃天理人伦之大体。而自天锡禹。以传于箕子。非己之所得而私者。安得不为武王陈之哉。且武王问道于箕子。则是武王以宾师待箕子。岂曰臣仆云乎。文山则有不然者。胡元以悖逆猾夏。殄灭正统。则已非武王顺天应人之举。而于文山为不共戴天之雠也。虽身无官位。而若备顾问于其左右。则是忘其不共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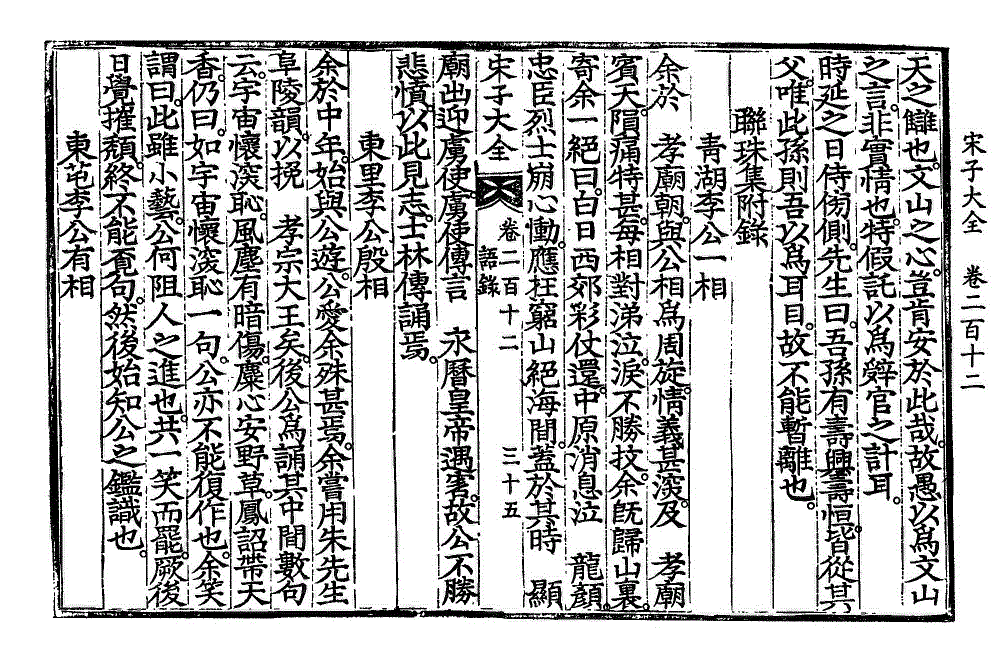 天之雠也。文山之心。岂肯安于此哉。故愚以为文山之言。非实情也。特假托以为辞官之计耳。
天之雠也。文山之心。岂肯安于此哉。故愚以为文山之言。非实情也。特假托以为辞官之计耳。时延之日侍傍侧。先生曰。吾孙有寿兴,寿恒。皆从其父。唯此孙则吾以为耳目。故不能暂离也。
联珠集附录
青湖李公一相
余于 孝庙朝。与公相为周旋。情义甚深。及 孝庙宾天。陨痛特甚。每相对涕泣。泪不胜抆。余既归山里。寄余一绝曰。白日西郊彩仗还。中原消息泣 龙颜。忠臣烈士崩心恸。应在穷山绝海间。盖于其时 显庙出迎虏使。虏使传言 永历皇帝遇害。故公不胜悲愤。以此见志。士林传诵焉。
东里李公殷相
余于中年。始与公游。公爱余殊甚焉。余尝用朱先生阜陵韵。以挽 孝宗大王矣。后公为诵其中间数句云。宇宙怀深耻。风尘有暗伤。麋心安野草。凤诏带天香。仍曰。如宇宙怀深耻一句。公亦不能复作也。余笑谓曰。此虽小艺。公何阻人之进也。共一笑而罢。厥后日觉摧颓。终不能觅句。然后始知公之鉴识也。
东芚李公有相
宋子大全卷二百十二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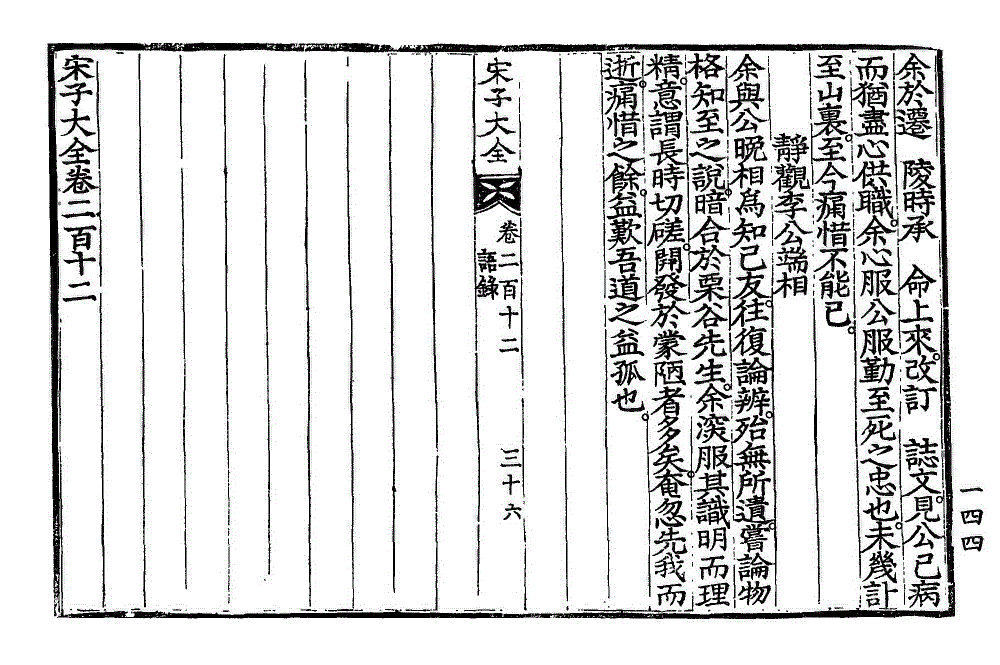 余于迁 陵时承 命上来。改订 志文。见公已病而犹尽心供职。余心服公服勤至死之忠也。未几讣至山里。至今痛惜不能已。
余于迁 陵时承 命上来。改订 志文。见公已病而犹尽心供职。余心服公服勤至死之忠也。未几讣至山里。至今痛惜不能已。静观李公端相
余与公晚相为知己友。往复论辨。殆无所遗。尝论物格知至之说。暗合于栗谷先生。余深服其识明而理精。意谓长时七磋。开发于蒙陋者多矣。奄忽先我而逝。痛惜之馀。益叹吾道之益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