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x 页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记
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5H 页
 观澜斋记(癸丑正月)
观澜斋记(癸丑正月)孟子有观水必观其澜之语。朱子取以为词。以赞孔子川上之叹。圣贤教人务本之意。可谓深矣。耽罗高生晦汝根旧居京城。自以尘纷烦聒。非所以养心看书之地。遂卜筑于南郊冠岳之下。结书架数椽。其南有小川横带。一日生来访余于洛阳山中而请其名。余曰。因其小川而名以观澜可乎。夫士之承师问道。欲成其仁者何限。而卒不能如其志者。无他。逐末而不务其本故也。今生以三圣贤之遗训。常目在之。自存心处己之间。以至于应事接物之际。莫不惟本之是务。则虽含章尚絅。晦木藏英。而其道自至于充大矣。比之水。其源甚微。而混混乎不舍昼夜。则其澜浑浩奔放。至于冲砥柱绝吕梁。而终极乎四海之远矣。然必须有谨独之功。然后能不间断而驯致乎纯亦不已之妙矣。不然则虽日观乎如斯者。而其在我者。则便相反戾而不相似矣。惜乎。朱子之词。其所以发挥其理者。必无馀蕴。而不传于世。只寂寥一句。独见于语类之书也。虽然。圣人所答问行问达之训。孟子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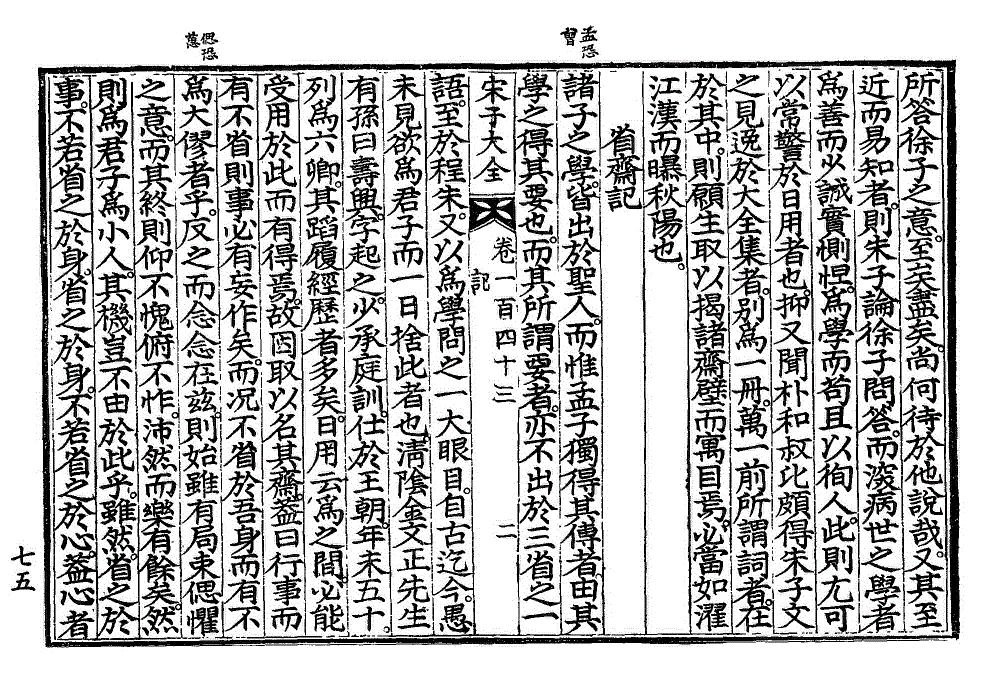 所答徐子之意。至矣尽矣。尚何待于他说哉。又其至近而易知者。则朱子论徐子问答。而深病世之学者为善而少诚实恻怛。为学而苟且以徇人。此则尤可以常警于日用者也。抑又闻朴和叔比颇得朱子文之见逸于大全集者。别为一册。万一前所谓词者。在于其中。则愿生取以揭诸斋壁而寓目焉。必当如濯江汉而曝秋阳也。
所答徐子之意。至矣尽矣。尚何待于他说哉。又其至近而易知者。则朱子论徐子问答。而深病世之学者为善而少诚实恻怛。为学而苟且以徇人。此则尤可以常警于日用者也。抑又闻朴和叔比颇得朱子文之见逸于大全集者。别为一册。万一前所谓词者。在于其中。则愿生取以揭诸斋壁而寓目焉。必当如濯江汉而曝秋阳也。省斋记
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而惟孟(孟恐曾)子独得其传者。由其学之得其要也。而其所谓要者。亦不出于三省之一语。至于程朱。又以为学问之一大眼目。自古迄今。愚未见欲为君子而一日舍此者也。清阴金文正先生有孙曰寿兴。字起之。少承庭训。仕于王朝。年未五十。列为六卿。其蹈履经历者多矣。日用云为之间。必能受用于此而有得焉。故因取以名其斋。盖曰行事而有不省则事必有妄作矣。而况不省于吾身而有不为大僇者乎。反之而念念在兹。则始虽有局束偲(偲恐葸)惧之意。而其终则仰不愧俯不怍。沛然而乐有馀矣。然则为君子为小人。其机岂不由于此乎。虽然。省之于事。不若省之于身。省之于身。不若省之于心。盖心者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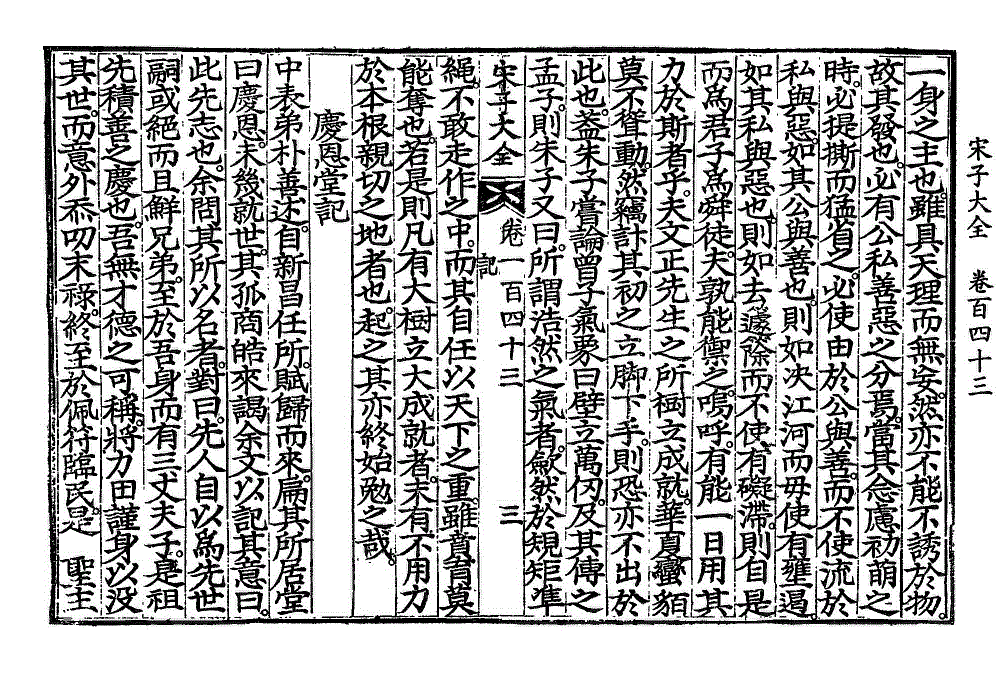 一身之主也。虽具天理而无妄。然亦不能不诱于物。故其发也。必有公私善恶之分焉。当其念虑初萌之时。必提撕而猛省之。必使由于公与善。而不使流于私与恶。如其公与善也。则如决江河而毋使有壅遏。如其私与恶也。则如去籧篨而不使有碍滞。则自是而为君子为舜徒。夫孰能御之。呜呼。有能一日用其力于斯者乎。夫文正先生之所树立成就。华夏蛮貊莫不耸动。然窃计其初之立脚下手。则恐亦不出于此也。盖朱子尝论曾子气象曰壁立万仞。及其传之孟子。则朱子又曰。所谓浩然之气者。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虽贲育莫能夺也。若是则凡有大树立大成就者。未有不用力于本根亲切之地者也。起之其亦终始勉之哉。
一身之主也。虽具天理而无妄。然亦不能不诱于物。故其发也。必有公私善恶之分焉。当其念虑初萌之时。必提撕而猛省之。必使由于公与善。而不使流于私与恶。如其公与善也。则如决江河而毋使有壅遏。如其私与恶也。则如去籧篨而不使有碍滞。则自是而为君子为舜徒。夫孰能御之。呜呼。有能一日用其力于斯者乎。夫文正先生之所树立成就。华夏蛮貊莫不耸动。然窃计其初之立脚下手。则恐亦不出于此也。盖朱子尝论曾子气象曰壁立万仞。及其传之孟子。则朱子又曰。所谓浩然之气者。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虽贲育莫能夺也。若是则凡有大树立大成就者。未有不用力于本根亲切之地者也。起之其亦终始勉之哉。庆恩堂记
中表弟朴善述。自新昌任所。赋归而来。扁其所居堂曰庆恩。未几就世。其孤商皓来谒余文以记其意曰。此先志也。余问其所以名者。对曰。先人自以为先世嗣或绝而且鲜兄弟。至于吾身而有三丈夫子。是祖先积善之庆也。吾无才德之可称。将力田谨身以没其世。而意外忝叨末禄。终至于佩符临民。是 圣主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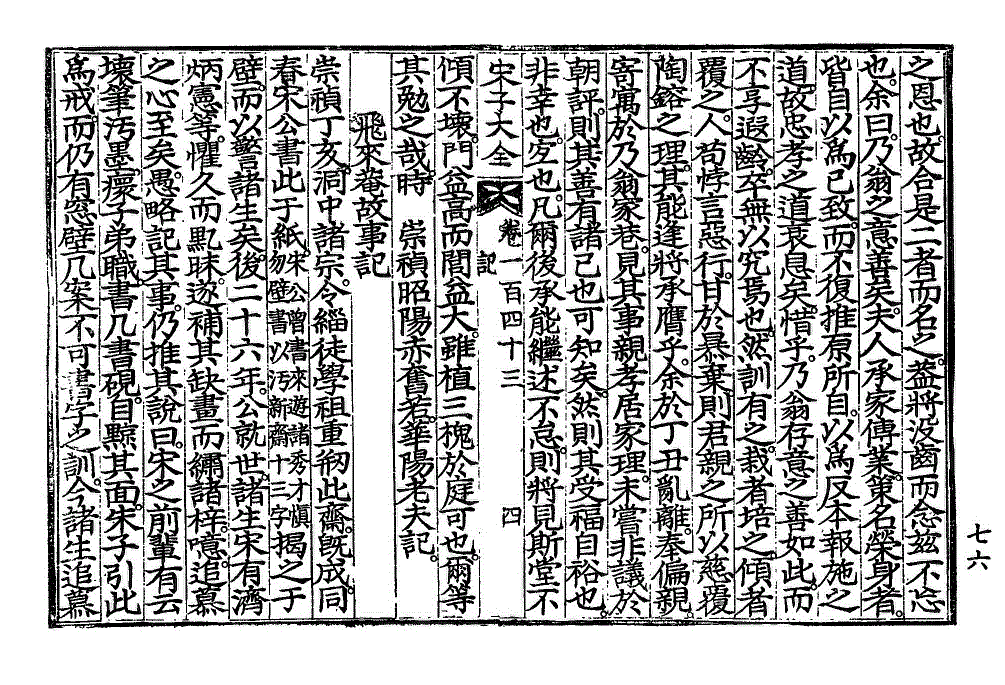 之恩也。故合是二者而名之。盖将没齿而念兹不忘也。余曰。乃翁之意善矣。夫人承家传业。策名荣身者。皆自以为己致。而不复推原所自。以为反本报施之道。故忠孝之道衰息矣。惜乎。乃翁存意之善如此。而不享遐龄。卒无以究焉也。然训有之。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人苟悖言恶行。甘于暴弃。则君亲之所以慈覆陶镕之理。其能逢将承膺乎。余于丁丑乱离。奉偏亲。寄寓于乃翁家巷。见其事亲孝居家理。未尝非议于朝评。则其善有诸己也可知矣。然则其受福自裕也。非幸也。宜也。凡尔后承能继述不怠。则将见斯堂不倾不坏。门益高而闾益大。虽植三槐于庭可也。尔等其勉之哉。时 崇祯昭阳赤奋若。华阳老夫记。
之恩也。故合是二者而名之。盖将没齿而念兹不忘也。余曰。乃翁之意善矣。夫人承家传业。策名荣身者。皆自以为己致。而不复推原所自。以为反本报施之道。故忠孝之道衰息矣。惜乎。乃翁存意之善如此。而不享遐龄。卒无以究焉也。然训有之。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人苟悖言恶行。甘于暴弃。则君亲之所以慈覆陶镕之理。其能逢将承膺乎。余于丁丑乱离。奉偏亲。寄寓于乃翁家巷。见其事亲孝居家理。未尝非议于朝评。则其善有诸己也可知矣。然则其受福自裕也。非幸也。宜也。凡尔后承能继述不怠。则将见斯堂不倾不坏。门益高而闾益大。虽植三槐于庭可也。尔等其勉之哉。时 崇祯昭阳赤奋若。华阳老夫记。飞来庵故事记
崇祯丁亥。洞中诸宗。令缁徒学祖重刱此斋。既成。同春宋公书此于纸。(宋公曾书来游诸秀才慎勿壁书以污新斋十三字)揭之于壁。而以警诸生矣。后二十六年。公就世。诸生宋有济炳宪等。惧久而䵝昧。遂补其缺画而绣诸梓。噫。追慕之心至矣。愚略记其事。仍推其说曰。宋之前辈有云坏笔污墨。瘝子弟职。书几书砚。自黥其面。朱子引此为戒。而仍有窗壁几案不可书字之训。今诸生追慕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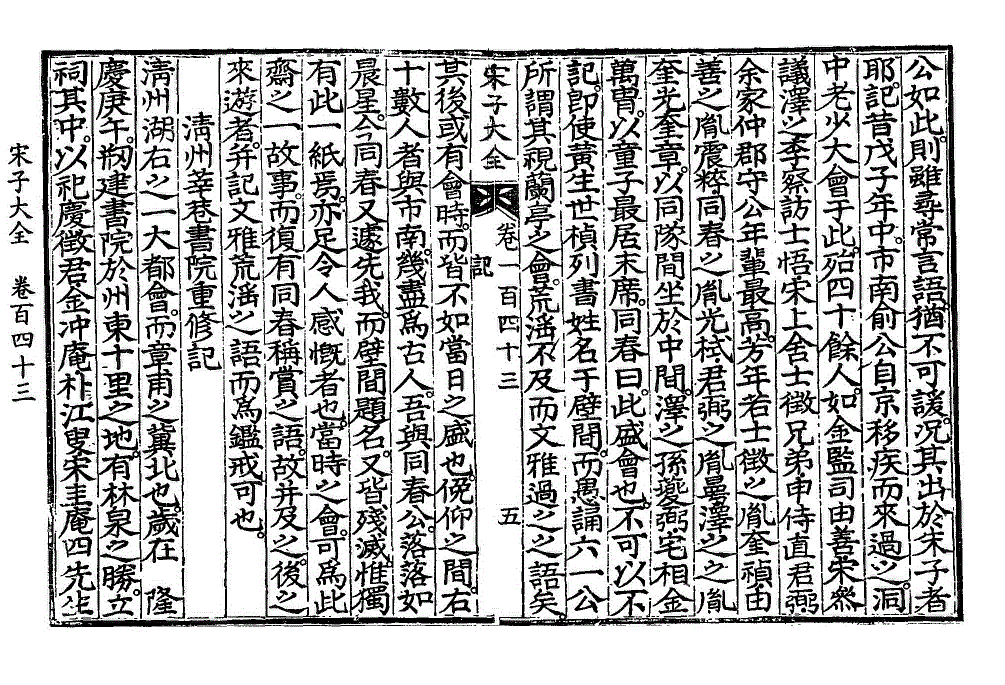 公如此。则虽寻常言语。犹不可谖。况其出于朱子者耶。记昔戊子年中。市南俞公自京移疾而来过之。洞中老少大会于此。殆四十馀人。如金监司由善,宋参议泽之,李察访士悟,宋上舍士徵兄弟,申侍直君弼,余家仲郡守公年辈最高。芳年若士徵之胤奎祯,由善之胤震粹,同春之胤光栻,君弼之胤曼,泽之之胤奎光,奎章。以同队间坐于中间。泽之孙夔弼,宅相金万胄。以童子最居末席。同春曰。此盛会也。不可以不记。即使黄生世桢列书姓名于壁间。而愚诵六一公所谓其视兰亭之会。荒淫不及而文雅过之之语矣。其后或有会时。而皆不如当日之盛也。俛仰之间。右十数人者与市南。几尽为古人。吾与同春公。落落如晨星。今同春又遽先我。而壁间题名。又皆残灭。惟独有此一纸焉。亦足令人感慨者也。当时之会。可为此斋之一故事。而复有同春称赏之语。故并及之。后之来游者。并记文雅荒淫之语而为鉴戒可也。
公如此。则虽寻常言语。犹不可谖。况其出于朱子者耶。记昔戊子年中。市南俞公自京移疾而来过之。洞中老少大会于此。殆四十馀人。如金监司由善,宋参议泽之,李察访士悟,宋上舍士徵兄弟,申侍直君弼,余家仲郡守公年辈最高。芳年若士徵之胤奎祯,由善之胤震粹,同春之胤光栻,君弼之胤曼,泽之之胤奎光,奎章。以同队间坐于中间。泽之孙夔弼,宅相金万胄。以童子最居末席。同春曰。此盛会也。不可以不记。即使黄生世桢列书姓名于壁间。而愚诵六一公所谓其视兰亭之会。荒淫不及而文雅过之之语矣。其后或有会时。而皆不如当日之盛也。俛仰之间。右十数人者与市南。几尽为古人。吾与同春公。落落如晨星。今同春又遽先我。而壁间题名。又皆残灭。惟独有此一纸焉。亦足令人感慨者也。当时之会。可为此斋之一故事。而复有同春称赏之语。故并及之。后之来游者。并记文雅荒淫之语而为鉴戒可也。清州莘巷书院重修记
清州湖右之一大都会。而章甫之冀北也。岁在 隆庆庚午。刱建书院于州东十里之地。有林泉之胜。立祠其中。以祀庆徵君,金冲庵,朴江叟,宋圭庵四先生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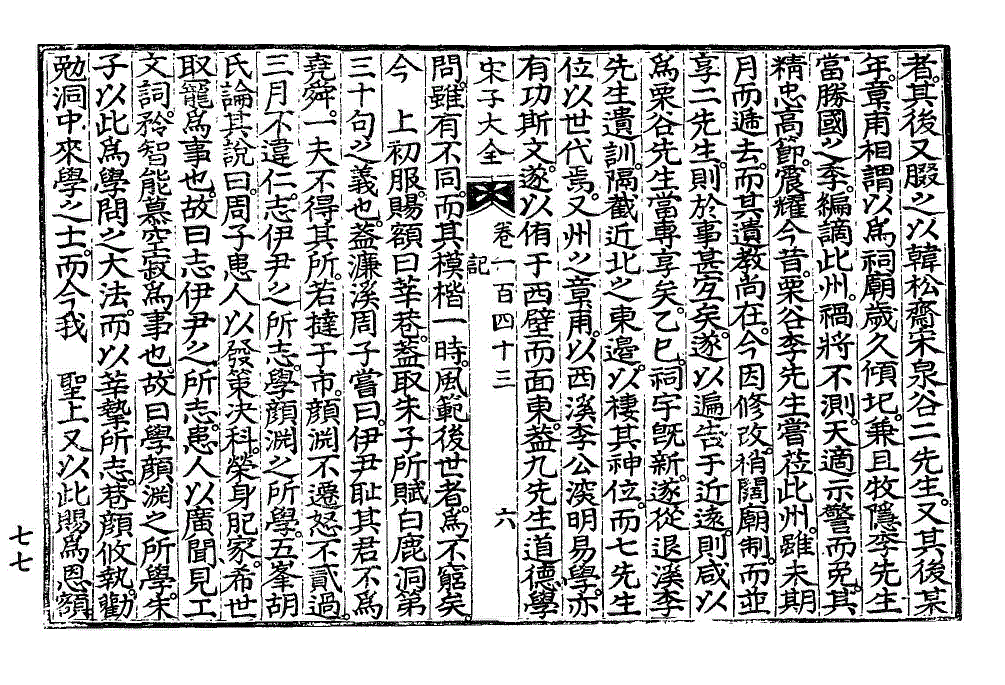 者。其后又啜之以韩松斋,宋泉谷二先生。又其后某年。章甫相谓以为祠庙岁久倾圮。兼且牧隐李先生当胜国之季。编谪此州。祸将不测。天适示警而免。其精忠高节。震耀今昔。栗谷李先生尝莅此州。虽未期月而递去。而其遗教尚在。今因修改。稍阔庙制。而并享二先生。则于事甚宜矣。遂以遍告于近远。则咸以为栗谷先生当专享矣。乙巳。祠宇既新。遂从退溪李先生遗训。隔截近北之东边。以栖其神位。而七先生位以世代焉。又州之章甫。以西溪李公深明易学。亦有功斯文。遂以侑于西壁而面东。盖九先生道德学问。虽有不同。而其模楷一时。风范后世者。为不穷矣。今 上初服。赐额曰莘巷。盖取朱子所赋白鹿洞第三十句之义也。盖濂溪,周子尝曰。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五峰胡氏论其说曰。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渊之所学。朱子以此为学问之大法。而以莘挚所志。巷颜攸执。劝勉洞中来学之士。而今我 圣上又以此赐为恩额。
者。其后又啜之以韩松斋,宋泉谷二先生。又其后某年。章甫相谓以为祠庙岁久倾圮。兼且牧隐李先生当胜国之季。编谪此州。祸将不测。天适示警而免。其精忠高节。震耀今昔。栗谷李先生尝莅此州。虽未期月而递去。而其遗教尚在。今因修改。稍阔庙制。而并享二先生。则于事甚宜矣。遂以遍告于近远。则咸以为栗谷先生当专享矣。乙巳。祠宇既新。遂从退溪李先生遗训。隔截近北之东边。以栖其神位。而七先生位以世代焉。又州之章甫。以西溪李公深明易学。亦有功斯文。遂以侑于西壁而面东。盖九先生道德学问。虽有不同。而其模楷一时。风范后世者。为不穷矣。今 上初服。赐额曰莘巷。盖取朱子所赋白鹿洞第三十句之义也。盖濂溪,周子尝曰。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五峰胡氏论其说曰。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渊之所学。朱子以此为学问之大法。而以莘挚所志。巷颜攸执。劝勉洞中来学之士。而今我 圣上又以此赐为恩额。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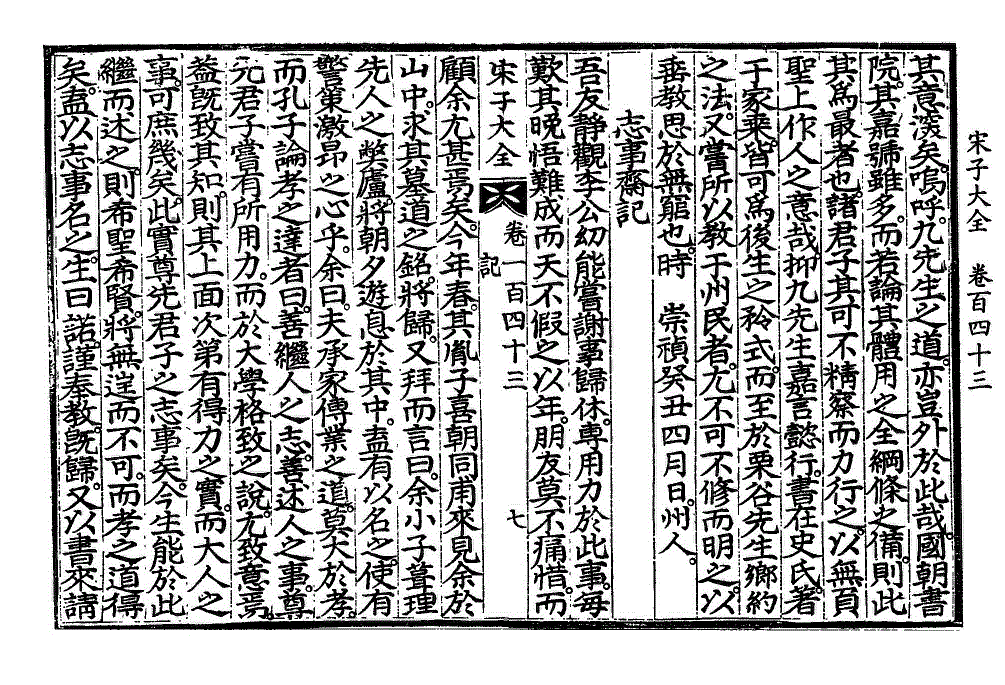 其意深矣。呜呼。九先生之道。亦岂外于此哉。国朝书院。其嘉号虽多。而若论其体用之全纲条之备。则此其为最者也。诸君子其可不精察而力行之。以无负圣上作人之意哉。抑九先生嘉言懿行。书在史氏。著于家乘。皆可为后生之矜式。而至于栗谷先生乡约之法。又尝所以教于州民者。尤不可不修而明之。以垂教思于无穷也。时 崇祯癸丑四月日。州人。
其意深矣。呜呼。九先生之道。亦岂外于此哉。国朝书院。其嘉号虽多。而若论其体用之全纲条之备。则此其为最者也。诸君子其可不精察而力行之。以无负圣上作人之意哉。抑九先生嘉言懿行。书在史氏。著于家乘。皆可为后生之矜式。而至于栗谷先生乡约之法。又尝所以教于州民者。尤不可不修而明之。以垂教思于无穷也。时 崇祯癸丑四月日。州人。志事斋记
吾友静观李公幼能尝谢事归休。专用力于此事。每叹其晚悟难成而天不假之以年。朋友莫不痛惜。而顾余尤甚焉矣。今年春。其胤子喜朝同甫来见余于山中。求其墓道之铭。将归。又拜而言曰。余小子葺理先人之弊庐。将朝夕游息于其中。盍有以名之。使有警策激昂之心乎。余曰。夫承家传业之道。莫大于孝。而孔子论孝之达者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尊先君子尝有所用力。而于大学格致之说。尤致意焉。盖既致其知。则其上面次第有得力之实。而大人之事。可庶几矣。此实尊先君子之志事矣。今生能于此继而述之。则希圣希贤。将无往而不可。而孝之道得矣。盍以志事名之。生曰诺。谨奉教。既归。又以书来请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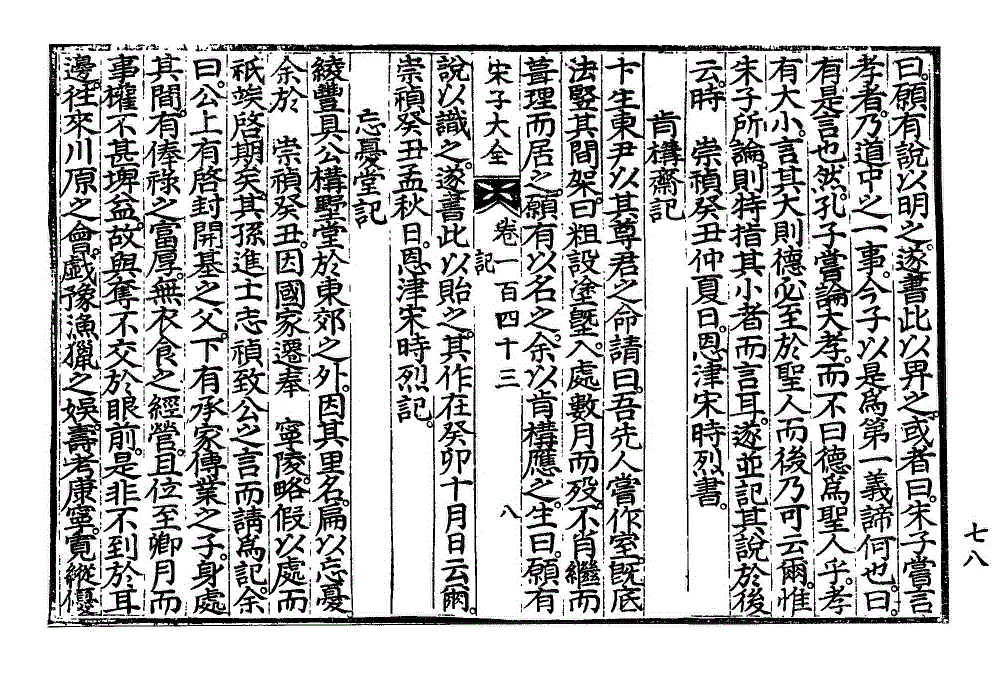 曰。愿有说以明之。遂书此以畀之。或者曰。朱子尝言孝者。乃道中之一事。今子以是为第一义谛何也。曰。有是言也然。孔子尝论大孝。而不曰德为圣人乎。孝有大小。言其大则德必至于圣人而后乃可云尔。惟朱子所论。则特指其小者而言耳。遂并记其说于后云。时 崇祯癸丑仲夏日。恩津宋时烈书。
曰。愿有说以明之。遂书此以畀之。或者曰。朱子尝言孝者。乃道中之一事。今子以是为第一义谛何也。曰。有是言也然。孔子尝论大孝。而不曰德为圣人乎。孝有大小。言其大则德必至于圣人而后乃可云尔。惟朱子所论。则特指其小者而言耳。遂并记其说于后云。时 崇祯癸丑仲夏日。恩津宋时烈书。肯构斋记
卞生东尹以其尊君之命请曰。吾先人尝作室。既底法竖其间架。曰粗设涂塈。入处数月而殁。不肖继而葺理而居之。愿有以名之。余以肯构应之。生曰。愿有说以识之。遂书此以贻之。其作在癸卯十月日云尔。崇祯癸丑孟秋日。恩津宋时烈记。
忘忧堂记
绫丰具公构墅堂于东郊之外。因其里名。扁以忘忧。余于 崇祯癸丑。因国家迁奉 宁陵。略假以处而祇俟启期矣。其孙进士志祯致公之言而请为记。余曰。公上有启封开基之父。下有承家传业之子。身处其间。有俸禄之富厚。无衣食之经营。且位至卿月而事权不甚埤益。故与夺不交于眼前。是非不到于耳边。往来川原之会。戏豫渔猎之娱。寿考康宁。宽纵优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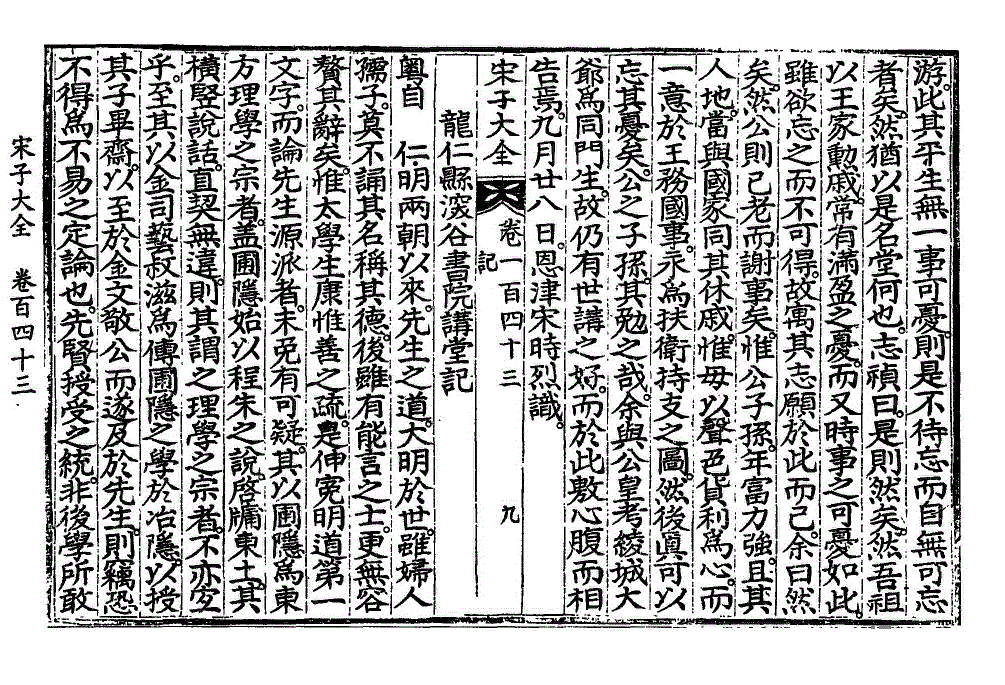 游。此其平生无一事可忧。则是不待忘而自无可忘者矣。然犹以是名堂何也。志祯曰。是则然矣。然吾祖以王家勋戚。常有满盈之忧。而又时事之可忧如此。虽欲忘之而不可得。故寓其志愿于此而已。余曰然矣。然公则已老而谢事矣。惟公子孙。年富力强。且其人地。当与国家同其休戚。惟毋以声色货利为心。而一意于王务国事。永为扶卫持支之图。然后真可以忘其忧矣。公之子孙。其勉之哉。余与公皇考绫城大爷为同门生。故仍有世讲之好。而于此敷心腹而相告焉。九月廿八日。恩津宋时烈识。
游。此其平生无一事可忧。则是不待忘而自无可忘者矣。然犹以是名堂何也。志祯曰。是则然矣。然吾祖以王家勋戚。常有满盈之忧。而又时事之可忧如此。虽欲忘之而不可得。故寓其志愿于此而已。余曰然矣。然公则已老而谢事矣。惟公子孙。年富力强。且其人地。当与国家同其休戚。惟毋以声色货利为心。而一意于王务国事。永为扶卫持支之图。然后真可以忘其忧矣。公之子孙。其勉之哉。余与公皇考绫城大爷为同门生。故仍有世讲之好。而于此敷心腹而相告焉。九月廿八日。恩津宋时烈识。龙仁县深谷书院讲堂记
粤自 仁,明两朝以来。先生之道。大明于世。虽妇人孺子。莫不诵其名称其德。后虽有能言之士。更无容赘其辞矣。惟太学生康惟善之疏。是伸冤明道第一文字。而论先生源派者。未免有可疑。其以圃隐为东方理学之宗者。盖圃隐始以程朱之说。启牖东土。其横竖说话。直契无违。则其谓之理学之宗者。不亦宜乎。至其以金司艺叔滋为传圃隐之学于冶隐。以授其子毕斋。以至于金文敬公而遂及于先生。则窃恐不得为不易之定论也。先贤授受之统。非后学所敢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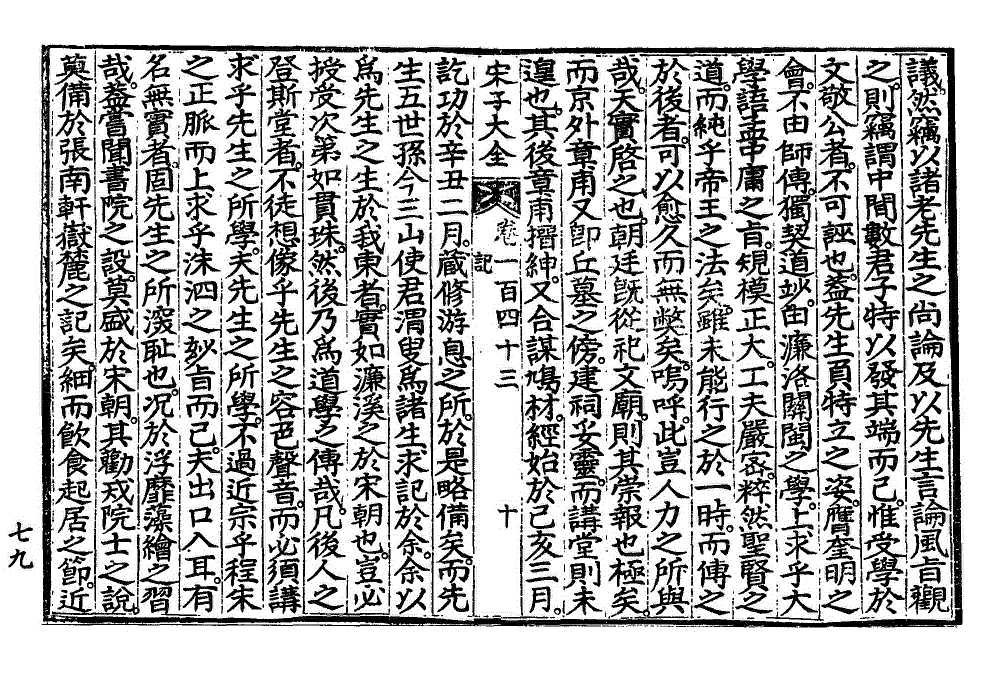 议。然窃以诸老先生之尚论及以先生言论风旨观之。则窃谓中间数君子特以发其端而已。惟受学于文敬公者。不可诬也。盖先生负特立之姿。膺奎明之会。不由师传。独契道妙。由濂洛关闽之学。上求乎大学,语,孟,中庸之旨。规模正大。工夫严密。粹然圣贤之道。而纯乎帝王之法矣。虽未能行之于一时。而传之于后者。可以愈久而无弊矣。呜呼。此岂人力之所与哉。天实启之也。朝廷既从祀文庙。则其崇报也极矣。而京外章甫又即丘墓之傍。建祠妥灵。而讲堂则未遑也。其后章甫搢绅。又合谋鸠材。经始于己亥三月。讫功于辛丑二月。藏修游息之所。于是略备矣。而先生五世孙今三山使君渭叟为诸生求记于余。余以为先生之生于我东者。实如濂溪之于宋朝也。岂必授受次第如贯珠。然后乃为道学之传哉。凡后人之登斯堂者。不徒想像乎先生之容色声音。而必须讲求乎先生之所学。夫先生之所学。不过近宗乎程朱之正脉而上求乎洙泗之妙旨而已。夫出口入耳。有名无实者。固先生之所深耻也。况于浮靡藻绘之习哉。盖尝闻书院之设。莫盛于宋朝。其劝戒院士之说。莫备于张南轩岳麓之记矣。细而饮食起居之节。近
议。然窃以诸老先生之尚论及以先生言论风旨观之。则窃谓中间数君子特以发其端而已。惟受学于文敬公者。不可诬也。盖先生负特立之姿。膺奎明之会。不由师传。独契道妙。由濂洛关闽之学。上求乎大学,语,孟,中庸之旨。规模正大。工夫严密。粹然圣贤之道。而纯乎帝王之法矣。虽未能行之于一时。而传之于后者。可以愈久而无弊矣。呜呼。此岂人力之所与哉。天实启之也。朝廷既从祀文庙。则其崇报也极矣。而京外章甫又即丘墓之傍。建祠妥灵。而讲堂则未遑也。其后章甫搢绅。又合谋鸠材。经始于己亥三月。讫功于辛丑二月。藏修游息之所。于是略备矣。而先生五世孙今三山使君渭叟为诸生求记于余。余以为先生之生于我东者。实如濂溪之于宋朝也。岂必授受次第如贯珠。然后乃为道学之传哉。凡后人之登斯堂者。不徒想像乎先生之容色声音。而必须讲求乎先生之所学。夫先生之所学。不过近宗乎程朱之正脉而上求乎洙泗之妙旨而已。夫出口入耳。有名无实者。固先生之所深耻也。况于浮靡藻绘之习哉。盖尝闻书院之设。莫盛于宋朝。其劝戒院士之说。莫备于张南轩岳麓之记矣。细而饮食起居之节。近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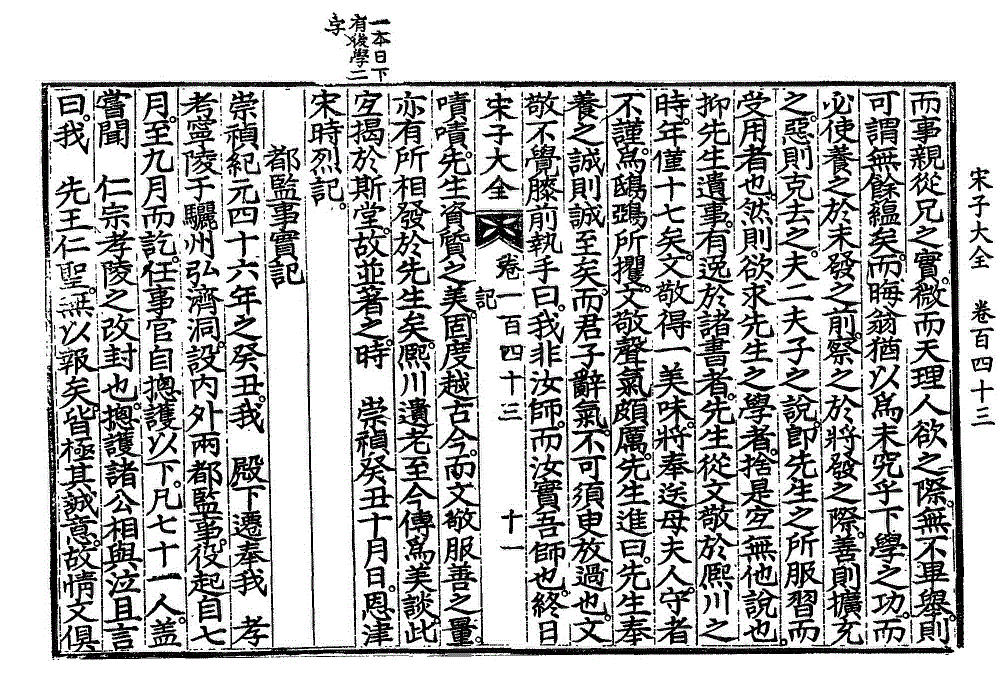 而事亲从兄之实。微而天理人欲之际。无不毕举。则可谓无馀蕴矣。而晦翁犹以为未究乎下学之功。而必使养之于未发之前。察之于将发之际。善则扩充之。恶则克去之。夫二夫子之说。即先生之所服习而受用者也。然则欲求先生之学者。舍是宜无他说也。抑先生遗事。有逸于诸书者。先生从文敬于熙川之时。年仅十七矣。文敬得一美味。将奉送母夫人。守者不谨。为鸱鸦所攫。文敬声气颇厉。先生进曰。先生奉养之诚则诚至矣。而君子辞气。不可须臾放过也。文敬不觉膝前执手曰。我非汝师。而汝实吾师也。终日啧啧。先生资质之美。固度越古今。而文敬服善之量。亦有所相发于先生矣。熙川遗老至今传为美谈。此宜揭于斯堂。故并著之。时 崇祯癸丑十月日(一本日下有后学二字)。恩津宋时烈记。
而事亲从兄之实。微而天理人欲之际。无不毕举。则可谓无馀蕴矣。而晦翁犹以为未究乎下学之功。而必使养之于未发之前。察之于将发之际。善则扩充之。恶则克去之。夫二夫子之说。即先生之所服习而受用者也。然则欲求先生之学者。舍是宜无他说也。抑先生遗事。有逸于诸书者。先生从文敬于熙川之时。年仅十七矣。文敬得一美味。将奉送母夫人。守者不谨。为鸱鸦所攫。文敬声气颇厉。先生进曰。先生奉养之诚则诚至矣。而君子辞气。不可须臾放过也。文敬不觉膝前执手曰。我非汝师。而汝实吾师也。终日啧啧。先生资质之美。固度越古今。而文敬服善之量。亦有所相发于先生矣。熙川遗老至今传为美谈。此宜揭于斯堂。故并著之。时 崇祯癸丑十月日(一本日下有后学二字)。恩津宋时烈记。都监事实记
崇祯纪元四十六年之癸丑。我 殿下迁奉我 孝考宁陵于骊州弘济洞。设内外两都监事。役起自七月。至九月而讫。任事官自总护以下。凡七十一人。盖尝闻 仁宗孝陵之改封也。总护诸公相与泣且言曰。我 先王仁圣。无以报矣。皆极其诚意。故情文俱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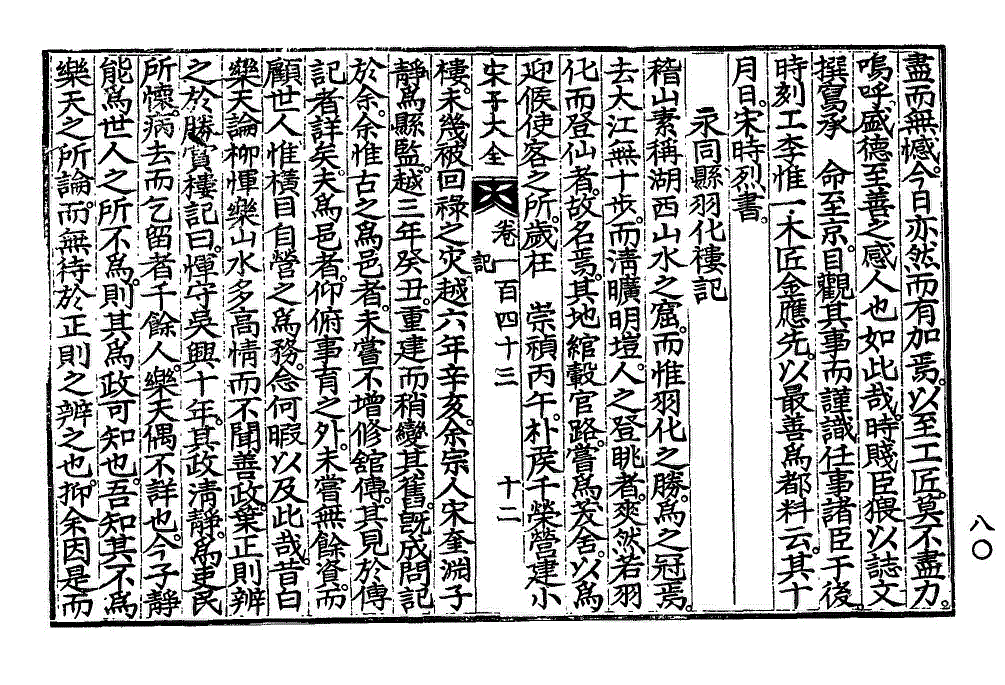 尽而无憾。今日亦然而有加焉。以至工匠。莫不尽力。呜呼。盛德至善之感人也如此哉。时贱臣猥以志文撰写承 命至京。目观其事而谨识任事诸臣于后。时刻工李惟一,木匠金应先。以最善为都料云。其十月日。宋时烈书。
尽而无憾。今日亦然而有加焉。以至工匠。莫不尽力。呜呼。盛德至善之感人也如此哉。时贱臣猥以志文撰写承 命至京。目观其事而谨识任事诸臣于后。时刻工李惟一,木匠金应先。以最善为都料云。其十月日。宋时烈书。永同县羽化楼记
稽山素称湖西山水之窟。而惟羽化之胜。为之冠焉。去大江无十步。而清旷明垲。人之登眺者。爽然若羽化而登仙者。故名焉。其地绾毂官路。尝为茇舍。以为迎候使客之所。岁在 崇祯丙午。朴侯千荣营建小楼。未几被回禄之灾。越六年辛亥。余宗人宋奎渊子静为县监。越三年癸丑。重建而稍变其旧。既成问记于余。余惟古之为邑者。未尝不增修馆传。其见于传记者详矣。夫为邑者。仰俯事育之外。未尝无馀资。而顾世人惟横目自营之为务。念何暇以及此哉。昔白乐天论柳恽乐山水多高情而不闻善政。叶正则辨之于胜赏楼记曰。恽守吴兴十年。其政清静。为吏民所怀。病去而乞留者千馀人。乐天偶不详也。今子静能为世人之所不为。则其为政可知也。吾知其不为乐天之所论。而无待于正则之辨之也。抑余因是而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1H 页
 又有所感也。范希文于岳阳楼记。自言求古仁人之心。而卒之以先忧后乐。至于朱夫子所记曲江楼。则想像前修。旷百世而相感。眷眷于是非邪正之际。忧悲愉怢。勃然于胸中。恍若亲见其人真闻其语。而卒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圣贤情思。虽于景致清绝之处。必在于民彝物则之中。而未尝有遗世独立招乔松揖浮丘之意。凡后之登斯楼者。必如登岳阳而忧范公之所忧。登曲江而感朱子之所感。则彼仙人之飘飘云天之外者。有不足羡。而名教之中自有真乐矣。愚既为子静而为正则之说。又为后之君子而为范公,朱子之说。而他有所不暇及焉。癸丑十一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又有所感也。范希文于岳阳楼记。自言求古仁人之心。而卒之以先忧后乐。至于朱夫子所记曲江楼。则想像前修。旷百世而相感。眷眷于是非邪正之际。忧悲愉怢。勃然于胸中。恍若亲见其人真闻其语。而卒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圣贤情思。虽于景致清绝之处。必在于民彝物则之中。而未尝有遗世独立招乔松揖浮丘之意。凡后之登斯楼者。必如登岳阳而忧范公之所忧。登曲江而感朱子之所感。则彼仙人之飘飘云天之外者。有不足羡。而名教之中自有真乐矣。愚既为子静而为正则之说。又为后之君子而为范公,朱子之说。而他有所不暇及焉。癸丑十一月日。恩津宋时烈记。咸兴府知乐亭记
昔琼州帅韩侯壁。作亭于放生池上。而取庄生语。名以知乐。朱夫子记之则曰。使邦人士女咏歌鼓舞。自乐其得被圣化而不愧于王民也。夫庄生以知鱼之乐为言。而夫子则以民之乐被王化为义。盖琼州在西南徼万里之外。鳞介之与居。獠猺之为邻。一朝闻教条之令礼让之说。其为乐也。岂不如幽谷者之出而迁乔耶。今我 圣上之十二年辛亥。以宜宁南公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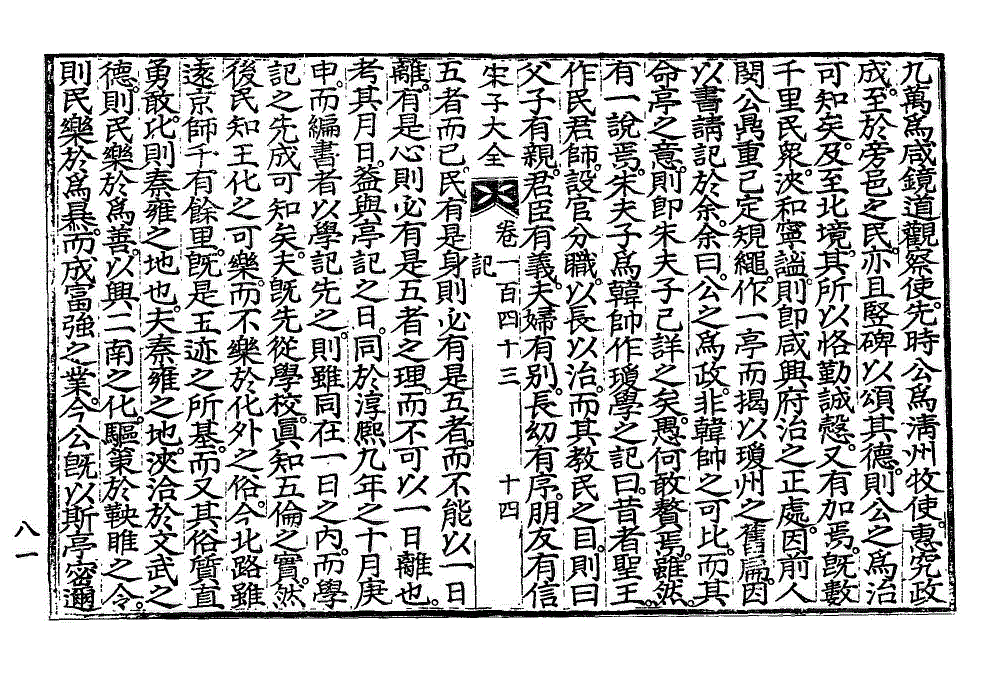 九万为咸镜道观察使。先时公为清州牧使。惠究政成。至于旁邑之民。亦且竖碑以颂其德。则公之为治可知矣。及至北境。其所以恪勤诚悫。又有加焉。既数千里民众。浃和宁谧。则即咸兴府治之正处。因前人闵公鼎重已定规绳。作一亭而揭以琼州之旧扁。因以书请记于余。余曰。公之为政。非韩帅之可比。而其命亭之意。则即朱夫子已详之矣。愚何敢赘焉。虽然。有一说焉。朱夫子为韩帅作琼学之记曰。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考其月日。盖与亭记之日。同于淳熙九年之十月庚申。而编书者以学记先之。则虽同在一日之内。而学记之先成可知矣。夫既先从学校。真知五伦之实。然后民知王化之可乐。而不乐于化外之俗。今北路虽远京师千有馀里。既是王迹之所基。而又其俗质直勇敢。比则秦雍之地也。夫秦雍之地。浃洽于文武之德。则民乐于为善。以兴二南之化。驱策于鞅睢之令。则民乐于为暴。而成富强之业。今公既以斯亭密迩
九万为咸镜道观察使。先时公为清州牧使。惠究政成。至于旁邑之民。亦且竖碑以颂其德。则公之为治可知矣。及至北境。其所以恪勤诚悫。又有加焉。既数千里民众。浃和宁谧。则即咸兴府治之正处。因前人闵公鼎重已定规绳。作一亭而揭以琼州之旧扁。因以书请记于余。余曰。公之为政。非韩帅之可比。而其命亭之意。则即朱夫子已详之矣。愚何敢赘焉。虽然。有一说焉。朱夫子为韩帅作琼学之记曰。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考其月日。盖与亭记之日。同于淳熙九年之十月庚申。而编书者以学记先之。则虽同在一日之内。而学记之先成可知矣。夫既先从学校。真知五伦之实。然后民知王化之可乐。而不乐于化外之俗。今北路虽远京师千有馀里。既是王迹之所基。而又其俗质直勇敢。比则秦雍之地也。夫秦雍之地。浃洽于文武之德。则民乐于为善。以兴二南之化。驱策于鞅睢之令。则民乐于为暴。而成富强之业。今公既以斯亭密迩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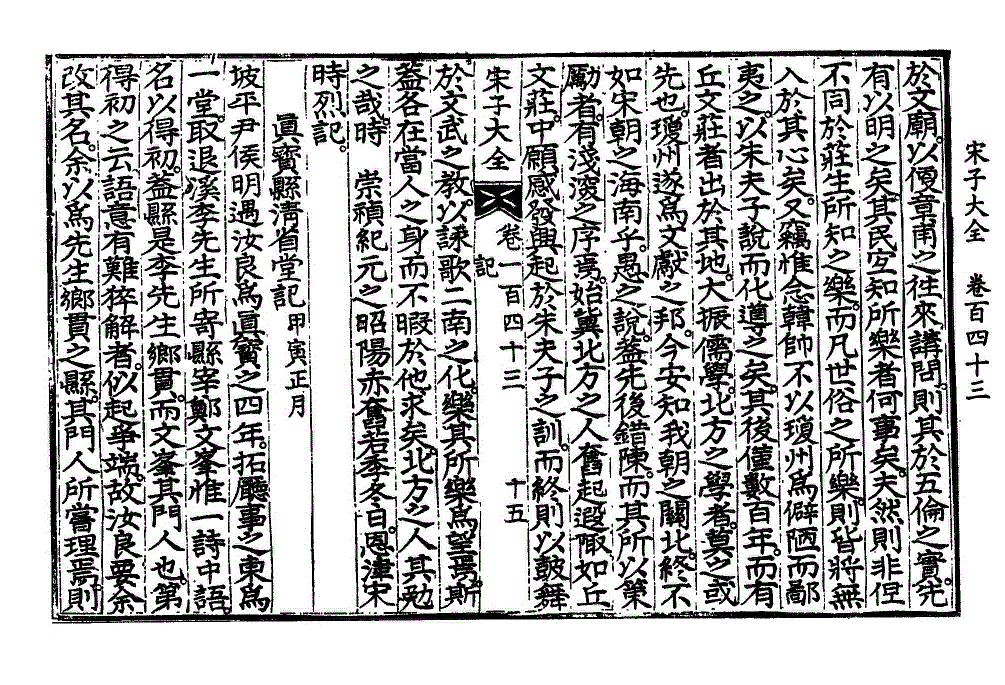 于文庙。以便章甫之往来讲问。则其于五伦之实。先有以明之矣。其民宜知所乐者何事矣。夫然则非但不同于庄生所知之乐。而凡世俗之所乐。则皆将无入于其心矣。又窃惟念韩帅不以琼州为僻陋而鄙夷之。以朱夫子说而化导之矣。其后仅数百年。而有丘文庄者出于其地。大振儒学。北方之学者。莫之或先也。琼州遂为文献之邦。今安知我朝之关北。终不如宋朝之海南乎。愚之说。盖先后错陈。而其所以策励者。有浅深之序焉。始冀北方之人奋起遐陬如丘文庄。中愿感发兴起于朱夫子之训。而终则以鼓舞于文武之教。以咏歌二南之化。乐其所乐为望焉。斯盖各在当人之身而不暇于他求矣。北方之人其勉之哉。时 崇祯纪元之昭阳赤奋若季冬日。恩津宋时烈记。
于文庙。以便章甫之往来讲问。则其于五伦之实。先有以明之矣。其民宜知所乐者何事矣。夫然则非但不同于庄生所知之乐。而凡世俗之所乐。则皆将无入于其心矣。又窃惟念韩帅不以琼州为僻陋而鄙夷之。以朱夫子说而化导之矣。其后仅数百年。而有丘文庄者出于其地。大振儒学。北方之学者。莫之或先也。琼州遂为文献之邦。今安知我朝之关北。终不如宋朝之海南乎。愚之说。盖先后错陈。而其所以策励者。有浅深之序焉。始冀北方之人奋起遐陬如丘文庄。中愿感发兴起于朱夫子之训。而终则以鼓舞于文武之教。以咏歌二南之化。乐其所乐为望焉。斯盖各在当人之身而不暇于他求矣。北方之人其勉之哉。时 崇祯纪元之昭阳赤奋若季冬日。恩津宋时烈记。真宝县清省堂记(甲寅正月)
坡平尹侯明遇汝良为真宝之四年。拓厅事之东为一堂。取退溪李先生所寄县宰郑文峰惟一诗中语。名以得初。盖县是李先生乡贯。而文峰其门人也。第得初之云。语意有难猝解者。似起争端。故汝良要余改其名。余以为先生乡贯之县。其门人所尝理焉。则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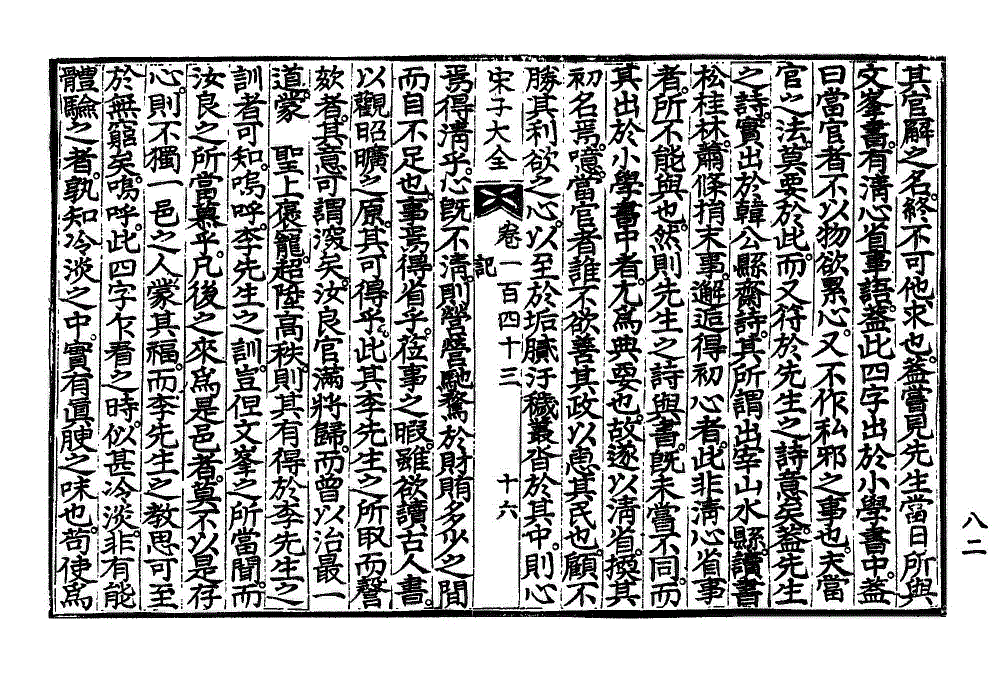 其官廨之名。终不可他求也。盖尝见先生当日所与文峰书。有清心省事语。盖此四字出于小学书中。盖曰当官者不以物欲累心。又不作私邪之事也。夫当官之法。莫要于此。而又符于先生之诗意矣。盖先生之诗。实出于韩公县斋诗。其所谓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者。此非清心省事者。所不能与也。然则先生之诗与书。既未尝不同。而其出于小学书中者。尤为典要也。故遂以清省。换其初名焉。噫。当官者谁不欲善其政以惠其民也。顾不胜其利欲之心。以至于垢腻污秽丛沓于其中。则心焉得清乎。心既不清。则营营驰骛于财贿多少之间而自不足也。事焉得省乎。莅事之暇。虽欲读古人书。以观昭旷之原。其可得乎。此其李先生之所取而謦欬者。其意可谓深矣。汝良官满将归。而曾以治最一道。蒙 圣上褒宠。超升高秩。则其有得于李先生之训者可知。呜呼。李先生之训。岂但文峰之所当闻。而汝良之所当慕乎。凡后之来为是邑者。莫不以是存心。则不独一邑之人蒙其福。而李先生之教思可至于无穷矣。呜呼。此四字乍看之时。似甚冷淡。非有能体验之者。孰知冷淡之中。实有真腴之味也。苟使为
其官廨之名。终不可他求也。盖尝见先生当日所与文峰书。有清心省事语。盖此四字出于小学书中。盖曰当官者不以物欲累心。又不作私邪之事也。夫当官之法。莫要于此。而又符于先生之诗意矣。盖先生之诗。实出于韩公县斋诗。其所谓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者。此非清心省事者。所不能与也。然则先生之诗与书。既未尝不同。而其出于小学书中者。尤为典要也。故遂以清省。换其初名焉。噫。当官者谁不欲善其政以惠其民也。顾不胜其利欲之心。以至于垢腻污秽丛沓于其中。则心焉得清乎。心既不清。则营营驰骛于财贿多少之间而自不足也。事焉得省乎。莅事之暇。虽欲读古人书。以观昭旷之原。其可得乎。此其李先生之所取而謦欬者。其意可谓深矣。汝良官满将归。而曾以治最一道。蒙 圣上褒宠。超升高秩。则其有得于李先生之训者可知。呜呼。李先生之训。岂但文峰之所当闻。而汝良之所当慕乎。凡后之来为是邑者。莫不以是存心。则不独一邑之人蒙其福。而李先生之教思可至于无穷矣。呜呼。此四字乍看之时。似甚冷淡。非有能体验之者。孰知冷淡之中。实有真腴之味也。苟使为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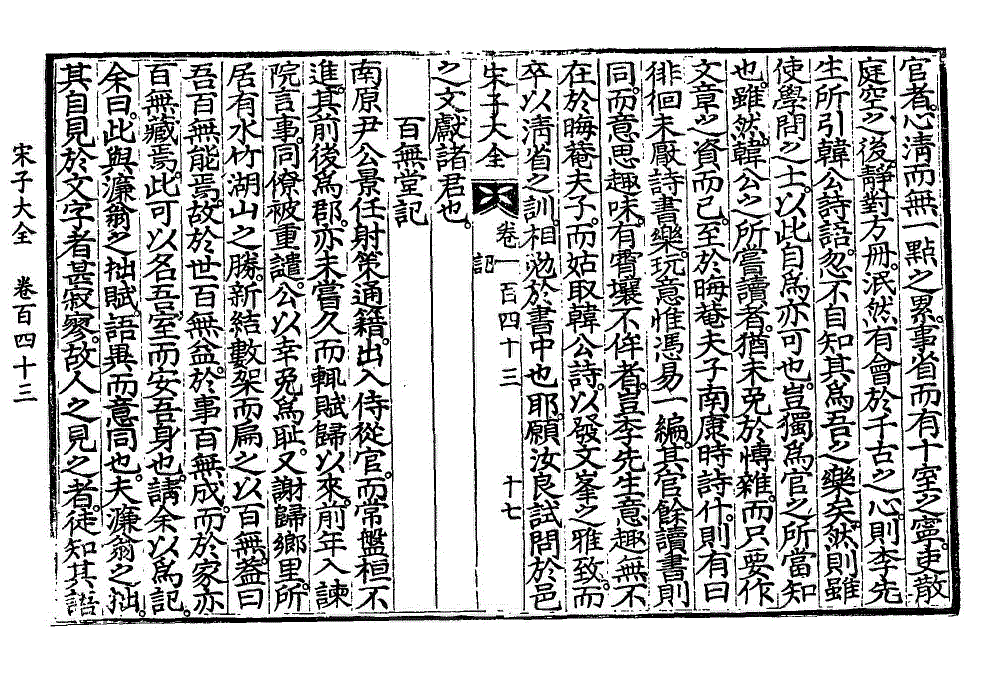 官者。心清而无一点之累。事省而有十室之宁。吏散庭空之后。静对方册。泯然有会于千古之心。则李先生所引韩公诗语。忽不自知其为吾之乐矣。然则虽使学问之士。以此自为亦可也。岂独为官之所当知也。虽然。韩公之所尝读者。犹未免于博杂。而只要作文章之资而已。至于晦庵夫子南康时诗什。则有曰徘徊未厌诗书乐。玩意惟凭易一编。其官馀读书则同。而意思趣味。有霄壤不侔者。岂李先生意趣无不在于晦庵夫子。而姑取韩公诗。以发文峰之雅致。而卒以清省之训。相勉于书中也耶。愿汝良试问于邑之文献诸君也。
官者。心清而无一点之累。事省而有十室之宁。吏散庭空之后。静对方册。泯然有会于千古之心。则李先生所引韩公诗语。忽不自知其为吾之乐矣。然则虽使学问之士。以此自为亦可也。岂独为官之所当知也。虽然。韩公之所尝读者。犹未免于博杂。而只要作文章之资而已。至于晦庵夫子南康时诗什。则有曰徘徊未厌诗书乐。玩意惟凭易一编。其官馀读书则同。而意思趣味。有霄壤不侔者。岂李先生意趣无不在于晦庵夫子。而姑取韩公诗。以发文峰之雅致。而卒以清省之训。相勉于书中也耶。愿汝良试问于邑之文献诸君也。百无堂记
南原尹公景任射策通籍。出入侍从官。而常盘桓不进。其前后为郡。亦未尝久而辄赋归以来。前年入谏院言事。同僚被重谴。公以幸免为耻。又谢归乡里。所居有水竹湖山之胜。新结数架而扁之以百无。盖曰吾百无能焉。故于世百无益。于事百无成。而于家亦百无藏焉。此可以名吾室而安吾身也。请余以为记。余曰。此与濂翁之拙赋。语异而意同也。夫濂翁之拙。其自见于文字者甚寂寥。故人之见之者。徒知其语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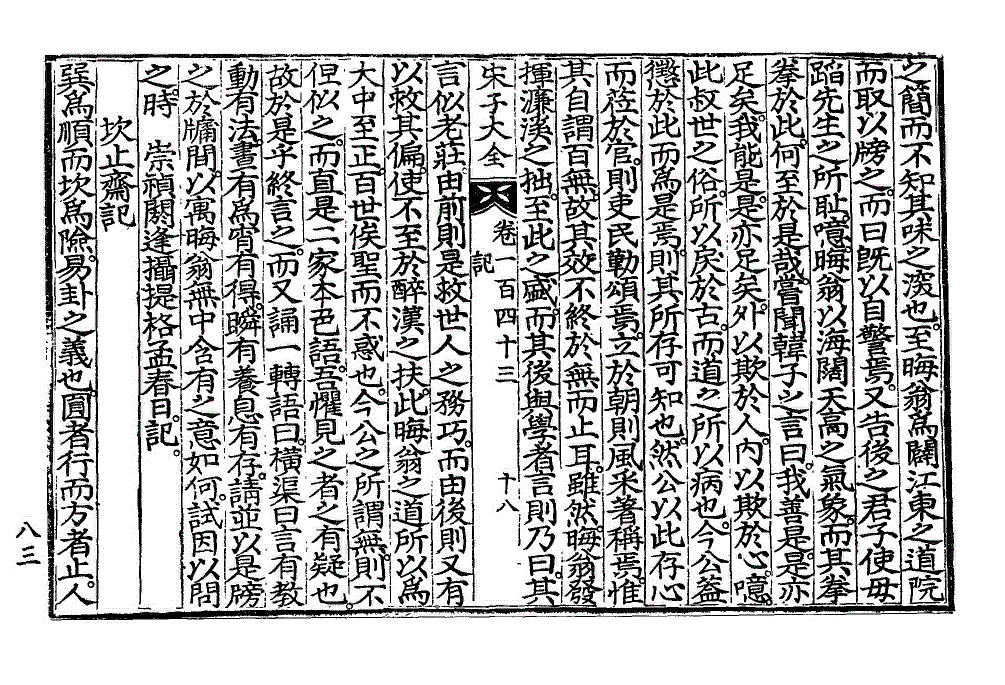 之简而不知其味之深也。至晦翁为辟江东之道院而取以榜之。而曰既以自警焉。又告后之君子使毋蹈先生之所耻。噫。晦翁以海阔天高之气象。而其拳拳于此。何至于是哉。尝闻韩子之言曰。我善是。是亦足矣。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噫。此叔世之俗。所以戾于古。而道之所以病也。今公盖惩于此而为是焉。则其所存可知也。然公以此存心而莅于官。则吏民勒颂焉。立于朝则风采著称焉。惟其自谓百无。故其效不终于无而止耳。虽然。晦翁发挥濂溪之拙。至此之盛。而其后与学者言则乃曰。其言似老庄。由前则是救世人之务巧。而由后则又有以救其偏。使不至于醉汉之扶。此晦翁之道所以为大中至正。百世俟圣而不惑也。今公之所谓无。则不但似之。而直是二家本色语。吾惧见之者之有疑也。故于是乎终言之。而又诵一转语曰。横渠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瞬有养息有存。请并以是榜之于牖间。以寓晦翁无中含有之意如何。试因以问之。时 崇祯阏逢摄提格孟春日。记。
之简而不知其味之深也。至晦翁为辟江东之道院而取以榜之。而曰既以自警焉。又告后之君子使毋蹈先生之所耻。噫。晦翁以海阔天高之气象。而其拳拳于此。何至于是哉。尝闻韩子之言曰。我善是。是亦足矣。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噫。此叔世之俗。所以戾于古。而道之所以病也。今公盖惩于此而为是焉。则其所存可知也。然公以此存心而莅于官。则吏民勒颂焉。立于朝则风采著称焉。惟其自谓百无。故其效不终于无而止耳。虽然。晦翁发挥濂溪之拙。至此之盛。而其后与学者言则乃曰。其言似老庄。由前则是救世人之务巧。而由后则又有以救其偏。使不至于醉汉之扶。此晦翁之道所以为大中至正。百世俟圣而不惑也。今公之所谓无。则不但似之。而直是二家本色语。吾惧见之者之有疑也。故于是乎终言之。而又诵一转语曰。横渠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瞬有养息有存。请并以是榜之于牖间。以寓晦翁无中含有之意如何。试因以问之。时 崇祯阏逢摄提格孟春日。记。坎止斋记
巽为顺而坎为险。易卦之义也。圆者行而方者止。人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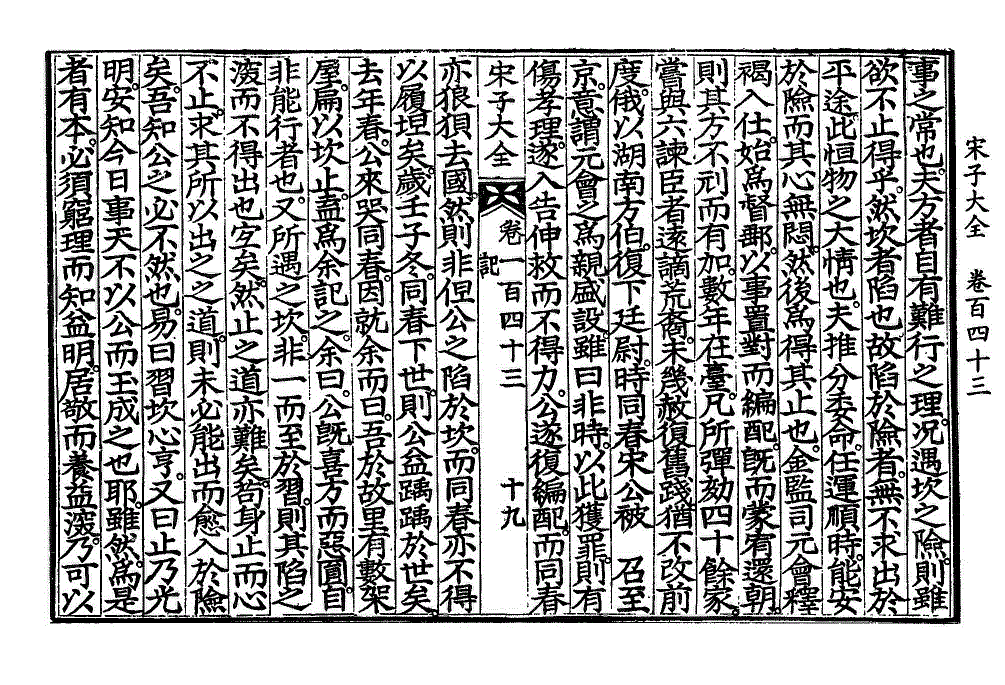 事之常也。夫方者自有难行之理。况遇坎之险。则虽欲不止得乎。然坎者陷也。故陷于险者。无不求出于平途。此恒物之大情也。夫推分委命。任运顺时。能安于险而其心无闷。然后为得其止也。金监司元会释褐入仕。始为督邮。以事置对而编配。既而蒙宥还朝。则其方不刓而有加。数年在台。凡所弹劾四十馀家。尝与六谏臣者远谪荒裔。未几赦复旧践。犹不改前度。俄以湖南方伯。复下廷尉。时同春宋公被 召至京。意谓元会之为亲盛设。虽曰非时。以此获罪。则有伤孝理。遂入告伸救而不得力。公遂复编配。而同春亦狼狈去国。然则非但公之陷于坎。而同春亦不得以履坦矣。岁壬子冬。同春下世。则公益踽踽于世矣。去年春。公来哭同春。因就余而曰。吾于故里有数架屋。扁以坎止。盍为余记之。余曰。公既喜方而恶圆。自非能行者也。又所遇之坎。非一而至于习。则其陷之深而不得出也宜矣。然止之道亦难矣。苟身止而心不止。求其所以出之之道。则未必能出而愈入于险矣。吾知公之必不然也。易曰习坎心亨。又曰止乃光明。安知今日事天不以公而玉成之也耶。虽然。为是者有本。必须穷理而知益明。居敬而养益深。乃可以
事之常也。夫方者自有难行之理。况遇坎之险。则虽欲不止得乎。然坎者陷也。故陷于险者。无不求出于平途。此恒物之大情也。夫推分委命。任运顺时。能安于险而其心无闷。然后为得其止也。金监司元会释褐入仕。始为督邮。以事置对而编配。既而蒙宥还朝。则其方不刓而有加。数年在台。凡所弹劾四十馀家。尝与六谏臣者远谪荒裔。未几赦复旧践。犹不改前度。俄以湖南方伯。复下廷尉。时同春宋公被 召至京。意谓元会之为亲盛设。虽曰非时。以此获罪。则有伤孝理。遂入告伸救而不得力。公遂复编配。而同春亦狼狈去国。然则非但公之陷于坎。而同春亦不得以履坦矣。岁壬子冬。同春下世。则公益踽踽于世矣。去年春。公来哭同春。因就余而曰。吾于故里有数架屋。扁以坎止。盍为余记之。余曰。公既喜方而恶圆。自非能行者也。又所遇之坎。非一而至于习。则其陷之深而不得出也宜矣。然止之道亦难矣。苟身止而心不止。求其所以出之之道。则未必能出而愈入于险矣。吾知公之必不然也。易曰习坎心亨。又曰止乃光明。安知今日事天不以公而玉成之也耶。虽然。为是者有本。必须穷理而知益明。居敬而养益深。乃可以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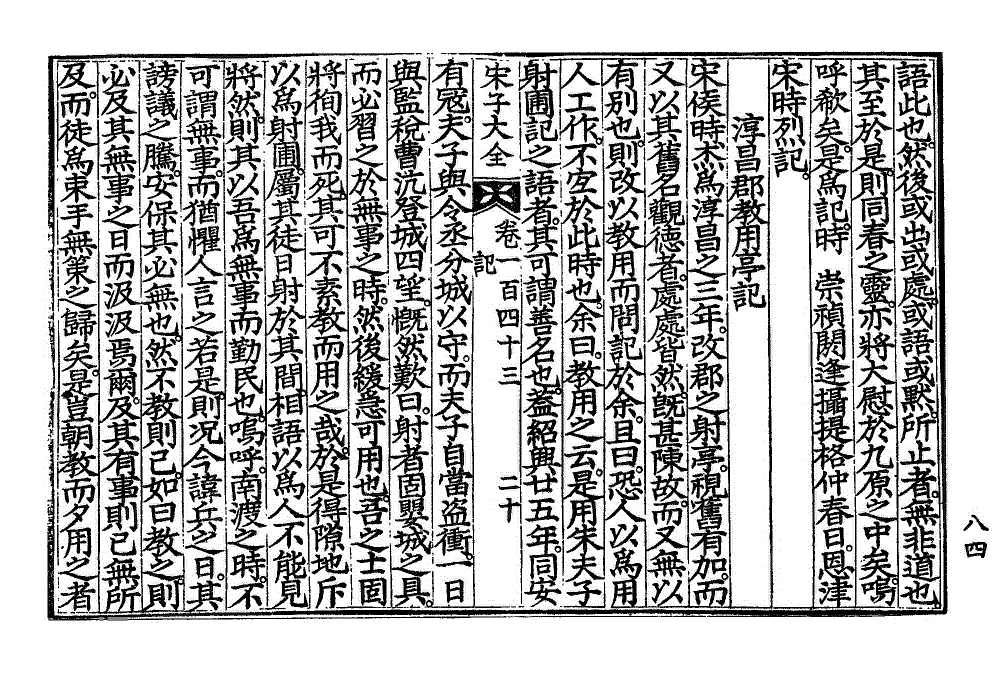 语此也。然后或出或处。或语或默。所止者。无非道也。其至于是。则同春之灵。亦将大慰于九原之中矣。呜呼欷矣。是为记。时 崇祯阏逢摄提格仲春日。恩津宋时烈记。
语此也。然后或出或处。或语或默。所止者。无非道也。其至于是。则同春之灵。亦将大慰于九原之中矣。呜呼欷矣。是为记。时 崇祯阏逢摄提格仲春日。恩津宋时烈记。淳昌郡教用亭记
宋侯时杰为淳昌之三年。改郡之射亭。视旧有加。而又以其旧名观德者。处处皆然。既甚陈故。而又无以有别也。则改以教用而问记于余。且曰。恐人以为用人工作。不宜于此时也。余曰。教用之云。是用朱夫子射圃记之语者。其可谓善名也。盖绍兴廿五年。同安有寇。夫子与令丞分城以守。而夫子自当盗冲。一日与监税曹沆登城四望。慨然叹曰。射者固婴城之具。而必习之于无事之时。然后缓急可用也。吾之士固将徇我而死。其可不素教而用之哉。于是得隙地斥以为射圃。属其徒日射于其间。相语以为人不能见将然。则其以吾为无事而勤民也。呜呼。南渡之时。不可谓无事。而犹惧人言之若是。则况今讳兵之日。其谤议之腾。安保其必无也。然不教则已。如曰教之。则必及其无事之日而汲汲焉尔。及其有事则已无所及。而徒为束手无策之归矣。是岂朝教而夕用之者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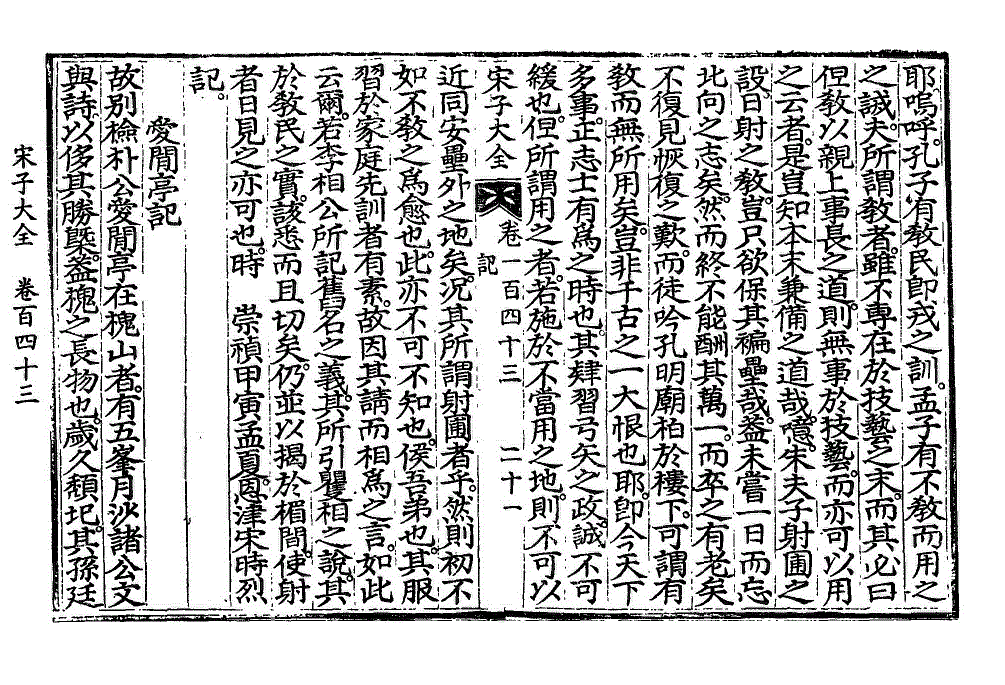 耶呜呼。孔子有教民即戎之训。孟子有不教而用之之诫。夫所谓教者。虽不专在于技艺之末。而其必曰但教以亲上事长之道。则无事于技艺。而亦可以用之云者。是岂知本末兼备之道哉。噫。朱夫子射圃之设。日射之教。岂只欲保其褊垒哉。盖未尝一日而忘北向之志矣。然而终不能酬其万一。而卒之有老矣不复见恢复之叹。而徒吟孔明庙柏于楼下。可谓有教而无所用矣。岂非千古之一大恨也耶。即今天下多事。正志士有为之时也。其肄习弓矢之政。诚不可缓也。但所谓用之者。若施于不当用之地。则不可以近同安垒外之地矣。况其所谓射圃者乎。然则初不如不教之为愈也。此亦不可不知也。侯吾弟也。其服习于家庭先训者有素。故因其请而相为之言。如此云尔。若李相公所记旧名之义。其所引矍相之说。其于教民之实。该悉而且切矣。仍并以揭于楣间。使射者日见之亦可也。时 崇祯甲寅孟夏。恩津宋时烈记。
耶呜呼。孔子有教民即戎之训。孟子有不教而用之之诫。夫所谓教者。虽不专在于技艺之末。而其必曰但教以亲上事长之道。则无事于技艺。而亦可以用之云者。是岂知本末兼备之道哉。噫。朱夫子射圃之设。日射之教。岂只欲保其褊垒哉。盖未尝一日而忘北向之志矣。然而终不能酬其万一。而卒之有老矣不复见恢复之叹。而徒吟孔明庙柏于楼下。可谓有教而无所用矣。岂非千古之一大恨也耶。即今天下多事。正志士有为之时也。其肄习弓矢之政。诚不可缓也。但所谓用之者。若施于不当用之地。则不可以近同安垒外之地矣。况其所谓射圃者乎。然则初不如不教之为愈也。此亦不可不知也。侯吾弟也。其服习于家庭先训者有素。故因其请而相为之言。如此云尔。若李相公所记旧名之义。其所引矍相之说。其于教民之实。该悉而且切矣。仍并以揭于楣间。使射者日见之亦可也。时 崇祯甲寅孟夏。恩津宋时烈记。爱閒亭记
故别检朴公爱閒亭在槐山者。有五峰,月沙诸公文与诗。以侈其胜槩。盖槐之长物也。岁久颓圮。其孙廷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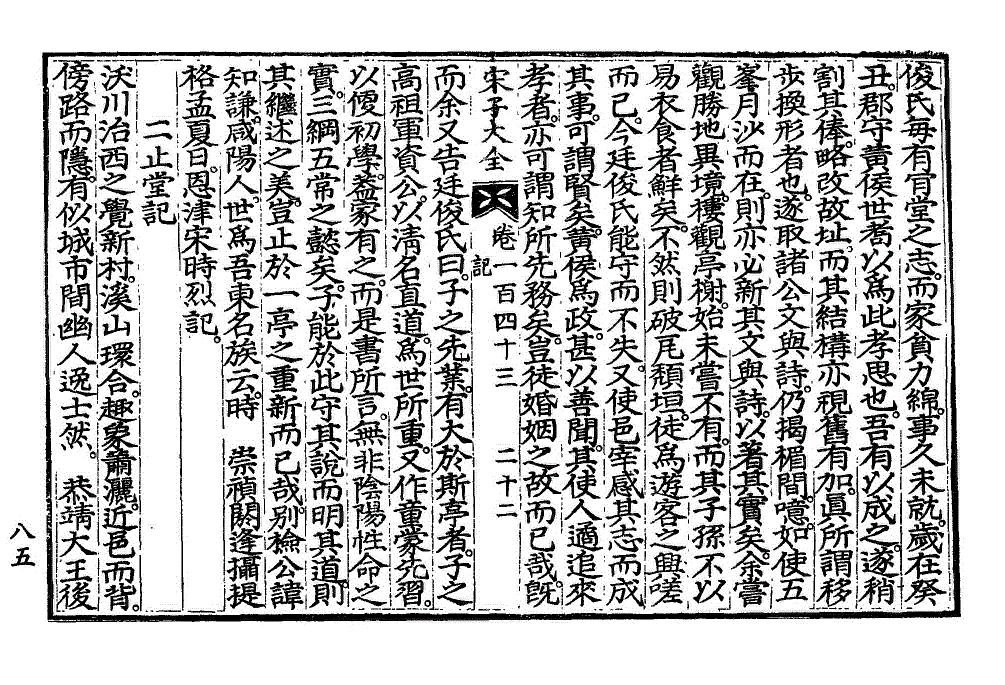 俊氏每有肯堂之志。而家贫力绵。事久未就。岁在癸丑。郡守黄侯世耇以为此孝思也。吾有以成之。遂稍割其俸。略改故址。而其结构亦视旧有加。真所谓移步换形者也。遂取诸公文与诗。仍揭楣间。噫。如使五峰,月沙而在。则亦必新其文与诗。以著其实矣。余尝观胜地异境。楼观亭榭。始未尝不有。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不然则破瓦颓垣。徒为游客之兴嗟而已。今廷俊氏能守而不失。又使邑宰感其志而成其事。可谓贤矣。黄侯为政。甚以善闻。其使人遹追来孝者。亦可谓知所先务矣。岂徒婚姻之故而已哉。既而余又告廷俊氏曰。子之先业。有大于斯亭者。子之高祖军资公。以清名直道。为世所重。又作童蒙先习。以便初学。盖家有之。而是书所言。无非阴阳性命之实。三纲五常之懿矣。子能于此守其说而明其道。则其继述之美。岂止于一亭之重新而已哉。别检公讳知谦。咸阳人。世为吾东名族云。时 崇祯阏逢摄提格孟夏日。恩津宋时烈记。
俊氏每有肯堂之志。而家贫力绵。事久未就。岁在癸丑。郡守黄侯世耇以为此孝思也。吾有以成之。遂稍割其俸。略改故址。而其结构亦视旧有加。真所谓移步换形者也。遂取诸公文与诗。仍揭楣间。噫。如使五峰,月沙而在。则亦必新其文与诗。以著其实矣。余尝观胜地异境。楼观亭榭。始未尝不有。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不然则破瓦颓垣。徒为游客之兴嗟而已。今廷俊氏能守而不失。又使邑宰感其志而成其事。可谓贤矣。黄侯为政。甚以善闻。其使人遹追来孝者。亦可谓知所先务矣。岂徒婚姻之故而已哉。既而余又告廷俊氏曰。子之先业。有大于斯亭者。子之高祖军资公。以清名直道。为世所重。又作童蒙先习。以便初学。盖家有之。而是书所言。无非阴阳性命之实。三纲五常之懿矣。子能于此守其说而明其道。则其继述之美。岂止于一亭之重新而已哉。别检公讳知谦。咸阳人。世为吾东名族云。时 崇祯阏逢摄提格孟夏日。恩津宋时烈记。二止堂记
沃川治西之觉新村。溪山环合。趣象萧洒。近邑而背。傍路而隐。有似城市间幽人逸士然。 恭靖大王后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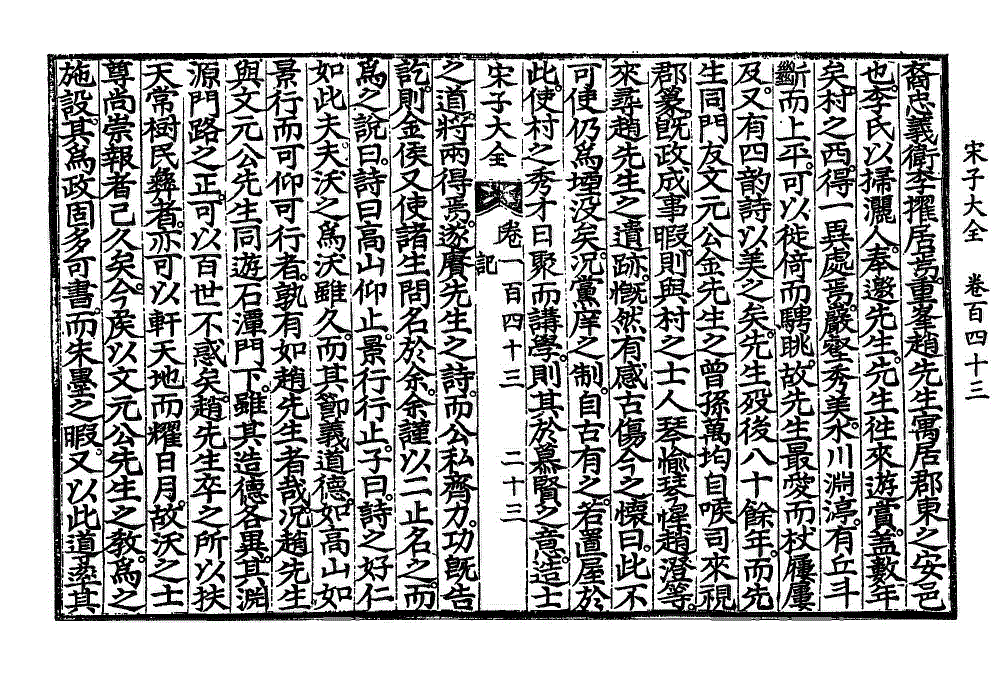 裔忠义卫李擢居焉。重峰赵先生寓居郡东之安邑也。李氏以扫洒人。奉邀先生。先生往来游赏。盖数年矣。村之西。得一异处焉。岩壑秀美。水川渊渟。有丘斗断而上平。可以徙倚而骋眺。故先生最爱而杖屦屡及。又有四韵诗以美之矣。先生殁后八十馀年。而先生同门友文元公金先生之曾孙万均自喉司来视郡篆。既政成事暇。则与村之士人琴愉,琴惺,赵澄等。来寻赵先生之遗迹。慨然有感古伤今之怀曰。此不可使仍为堙没矣。况党庠之制。自古有之。若置屋于此。使村之秀才日聚而讲学。则其于慕贤之意。造士之道。将两得焉。遂赓先生之诗。而公私齐力。功既告讫。则金侯又使诸生问名于余。余谨以二止名之。而为之说曰。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夫。夫沃之为沃虽久。而其节义道德。如高山如景行而可仰可行者。孰有如赵先生者哉。况赵先生与文元公先生同游石潭门下。虽其造德各异。其渊源门路之正。可以百世不惑矣。赵先生卒之所以扶天常树民彝者。亦可以轩天地而耀日月。故沃之士尊尚崇报者已久矣。今侯以文元公先生之教。为之施设。其为政固多可书。而朱墨之暇。又以此导率其
裔忠义卫李擢居焉。重峰赵先生寓居郡东之安邑也。李氏以扫洒人。奉邀先生。先生往来游赏。盖数年矣。村之西。得一异处焉。岩壑秀美。水川渊渟。有丘斗断而上平。可以徙倚而骋眺。故先生最爱而杖屦屡及。又有四韵诗以美之矣。先生殁后八十馀年。而先生同门友文元公金先生之曾孙万均自喉司来视郡篆。既政成事暇。则与村之士人琴愉,琴惺,赵澄等。来寻赵先生之遗迹。慨然有感古伤今之怀曰。此不可使仍为堙没矣。况党庠之制。自古有之。若置屋于此。使村之秀才日聚而讲学。则其于慕贤之意。造士之道。将两得焉。遂赓先生之诗。而公私齐力。功既告讫。则金侯又使诸生问名于余。余谨以二止名之。而为之说曰。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夫。夫沃之为沃虽久。而其节义道德。如高山如景行而可仰可行者。孰有如赵先生者哉。况赵先生与文元公先生同游石潭门下。虽其造德各异。其渊源门路之正。可以百世不惑矣。赵先生卒之所以扶天常树民彝者。亦可以轩天地而耀日月。故沃之士尊尚崇报者已久矣。今侯以文元公先生之教。为之施设。其为政固多可书。而朱墨之暇。又以此导率其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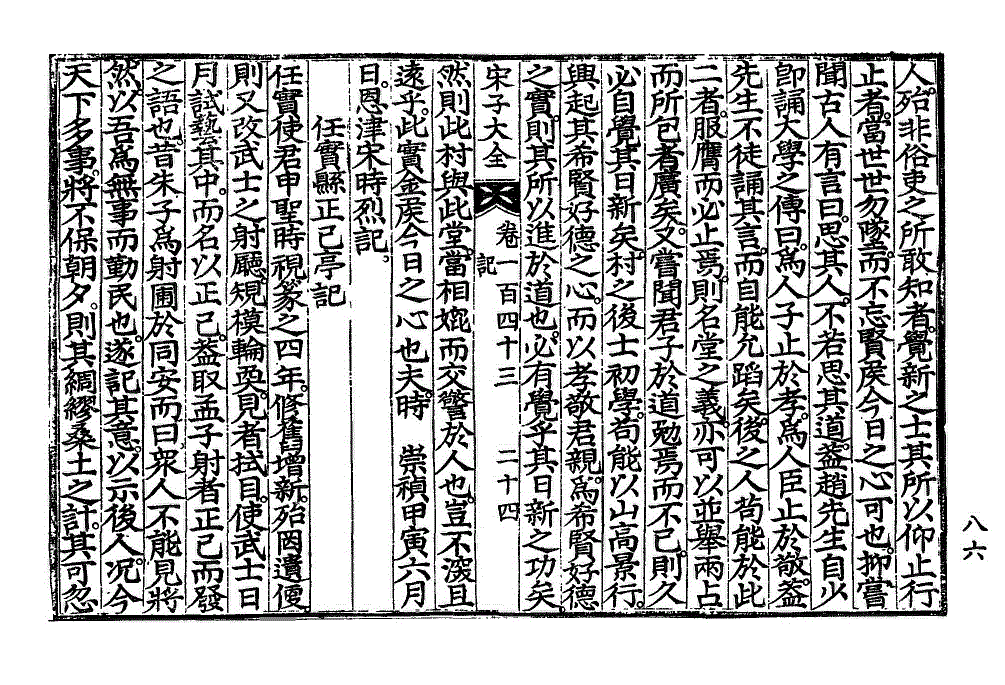 人。殆非俗吏之所敢知者。觉新之士其所以仰止行止者。当世世勿坠。而不忘贤侯今日之心可也。抑尝闻古人有言曰。思其人。不若思其道。盖赵先生自少即诵大学之传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臣止于敬。盖先生不徒诵其言。而自能允蹈矣。后之人苟能于此二者。服膺而必止焉。则名堂之义。亦可以并举两占而所包者广矣。又尝闻君子于道勉焉而不已。则久必自觉其日新矣。村之后士初学。苟能以山高景行。兴起其希贤好德之心。而以孝敬君亲。为希贤好德之实。则其所以进于道也。必有觉乎其日新之功矣。然则此村与此堂。当相媲而交警于人也。岂不深且远乎。此实金侯今日之心也夫。时 崇祯甲寅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人。殆非俗吏之所敢知者。觉新之士其所以仰止行止者。当世世勿坠。而不忘贤侯今日之心可也。抑尝闻古人有言曰。思其人。不若思其道。盖赵先生自少即诵大学之传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臣止于敬。盖先生不徒诵其言。而自能允蹈矣。后之人苟能于此二者。服膺而必止焉。则名堂之义。亦可以并举两占而所包者广矣。又尝闻君子于道勉焉而不已。则久必自觉其日新矣。村之后士初学。苟能以山高景行。兴起其希贤好德之心。而以孝敬君亲。为希贤好德之实。则其所以进于道也。必有觉乎其日新之功矣。然则此村与此堂。当相媲而交警于人也。岂不深且远乎。此实金侯今日之心也夫。时 崇祯甲寅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任实县正己亭记
任实使君申圣时视篆之四年。修旧增新。殆罔遗便。则又改武士之射厅。规模轮奂。见者拭目。使武士日月试艺其中。而名以正己。盖取孟子射者正己而发之语也。昔朱子为射圃于同安而曰。众人不能见将然。以吾为无事而勤民也。遂记其意。以示后人。况今天下多事。将不保朝夕。则其绸缪桑土之计。其可忽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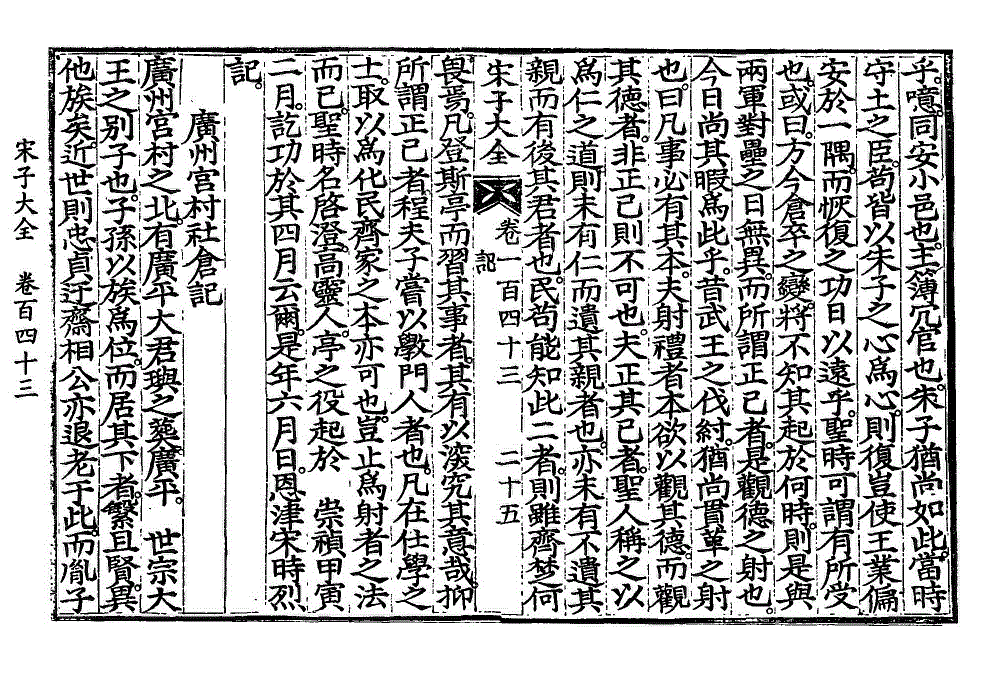 乎。噫。同安小邑也。主簿冗官也。朱子犹尚如此。当时守土之臣。苟皆以朱子之心为心。则复岂使王业偏安于一隅。而恢复之功日以远乎。圣时可谓有所受也。或曰。方今仓卒之变。将不知其起于何时。则是与两军对垒之日无异。而所谓正己者。是观德之射也。今日尚其暇为此乎。昔武王之伐纣。犹尚贯革之射也。曰凡事必有其本。夫射礼者本欲以观其德。而观其德者。非正己则不可也。夫正其己者。圣人称之以为仁之道。则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亦未有不遗其亲而有后其君者也。民苟能知此二者。则虽齐楚何畏焉。凡登斯亭而习其事者。其有以深究其意哉。抑所谓正己者。程夫子尝以敩门人者也。凡在仕学之士。取以为化民齐家之本亦可也。岂止为射者之法而已。圣时名启澄。高灵人。亭之役起于 崇祯甲寅二月。讫功于其四月云尔。是年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乎。噫。同安小邑也。主簿冗官也。朱子犹尚如此。当时守土之臣。苟皆以朱子之心为心。则复岂使王业偏安于一隅。而恢复之功日以远乎。圣时可谓有所受也。或曰。方今仓卒之变。将不知其起于何时。则是与两军对垒之日无异。而所谓正己者。是观德之射也。今日尚其暇为此乎。昔武王之伐纣。犹尚贯革之射也。曰凡事必有其本。夫射礼者本欲以观其德。而观其德者。非正己则不可也。夫正其己者。圣人称之以为仁之道。则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亦未有不遗其亲而有后其君者也。民苟能知此二者。则虽齐楚何畏焉。凡登斯亭而习其事者。其有以深究其意哉。抑所谓正己者。程夫子尝以敩门人者也。凡在仕学之士。取以为化民齐家之本亦可也。岂止为射者之法而已。圣时名启澄。高灵人。亭之役起于 崇祯甲寅二月。讫功于其四月云尔。是年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广州宫村社仓记
广州宫村之北。有广平大君玙之葬。广平。 世宗大王之别子也。子孙以族为位。而居其下者。繁且贤。异他族矣。近世则忠贞迂斋相公亦退老于此。而胤子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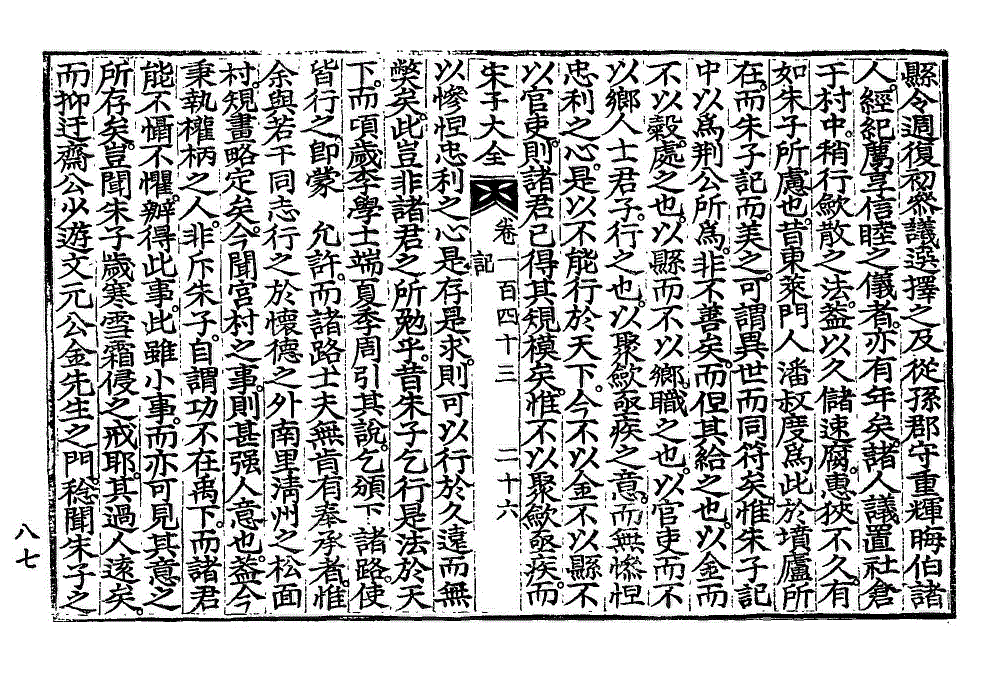 县令周复初,参议选择之及从孙郡守重辉,晦伯诸人。经纪荐享信睦之仪者。亦有年矣。诸人议置社仓于村中。稍行敛散之法。盖以久储速腐。惠狭不久。有如朱子所虑也。昔东莱门人潘叔度为此于坟庐所在。而朱子记而美之。可谓异世而同符矣。惟朱子记中以为荆公所为。非不善矣。而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无惨怛忠利之心。是以不能行于天下。今不以金不以县不以官吏。则诸君已得其规模矣。惟不以聚敛亟疾。而以惨怛忠利之心是存是求。则可以行于久远而无弊矣。此岂非诸君之所勉乎。昔朱子乞行是法于天下。而顷岁李学士端夏季周引其说。乞颁下诸路。使皆行之。即蒙 允许。而诸路士夫无肯有奉承者。惟余与若干同志行之于怀德之外南里,清州之松面村。规画略定矣。今闻宫村之事。则甚强人意也。盖今秉执权柄之人。非斥朱子。自谓功不在禹下。而诸君能不慑不惧。办得此事。此虽小事。而亦可见其意之所存矣。岂闻朱子岁寒雪霜侵之戒耶。其过人远矣。而抑迂斋公少游文元公金先生之门。稔闻朱子之
县令周复初,参议选择之及从孙郡守重辉,晦伯诸人。经纪荐享信睦之仪者。亦有年矣。诸人议置社仓于村中。稍行敛散之法。盖以久储速腐。惠狭不久。有如朱子所虑也。昔东莱门人潘叔度为此于坟庐所在。而朱子记而美之。可谓异世而同符矣。惟朱子记中以为荆公所为。非不善矣。而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无惨怛忠利之心。是以不能行于天下。今不以金不以县不以官吏。则诸君已得其规模矣。惟不以聚敛亟疾。而以惨怛忠利之心是存是求。则可以行于久远而无弊矣。此岂非诸君之所勉乎。昔朱子乞行是法于天下。而顷岁李学士端夏季周引其说。乞颁下诸路。使皆行之。即蒙 允许。而诸路士夫无肯有奉承者。惟余与若干同志行之于怀德之外南里,清州之松面村。规画略定矣。今闻宫村之事。则甚强人意也。盖今秉执权柄之人。非斥朱子。自谓功不在禹下。而诸君能不慑不惧。办得此事。此虽小事。而亦可见其意之所存矣。岂闻朱子岁寒雪霜侵之戒耶。其过人远矣。而抑迂斋公少游文元公金先生之门。稔闻朱子之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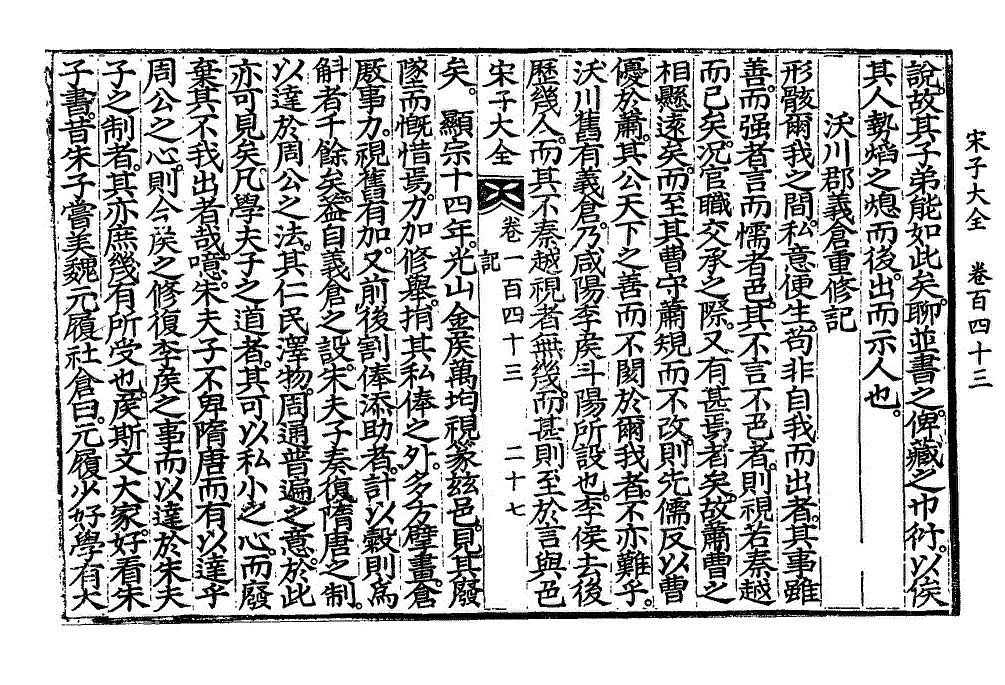 说。故其子弟能如此矣。聊并书之。俾藏之巾衍。以俟其人势焰之熄而后。出而示人也。
说。故其子弟能如此矣。聊并书之。俾藏之巾衍。以俟其人势焰之熄而后。出而示人也。沃川郡义仓重修记
形骸尔我之间。私意便生。苟非自我而出者。其事虽善。而强者言而懦者色。其不言不色者。则视若秦越而已矣。况官职交承之际。又有甚焉者矣。故萧,曹之相悬远矣。而至其曹守萧规而不改。则先儒反以曹优于萧。其公天下之善而不阂于尔我者。不亦难乎。沃川旧有义仓。乃咸阳李侯斗阳所设也。李侯去后历几人。而其不秦越视者无几。而甚则至于言与色矣。 显宗十四年。光山金侯万均视篆玆邑。见其废坠而慨惜焉。力加修举。捐其私俸之外。多方擘画。仓廒事力。视旧有加。又前后割俸添助者。计以谷则为斛者千馀矣。盖自义仓之设。朱夫子奏复隋唐之制。以达于周公之法。其仁民泽物。周通普遍之意。于此亦可见矣。凡学夫子之道者。其可以私小之心。而废弃其不我出者哉。噫。朱夫子不卑隋唐而有以达乎周公之心。则今侯之修复李侯之事而以达于朱夫子之制者。其亦庶几有所受也。侯斯文大家。好看朱子书。昔朱子尝美魏元履社仓曰。元履少好学有大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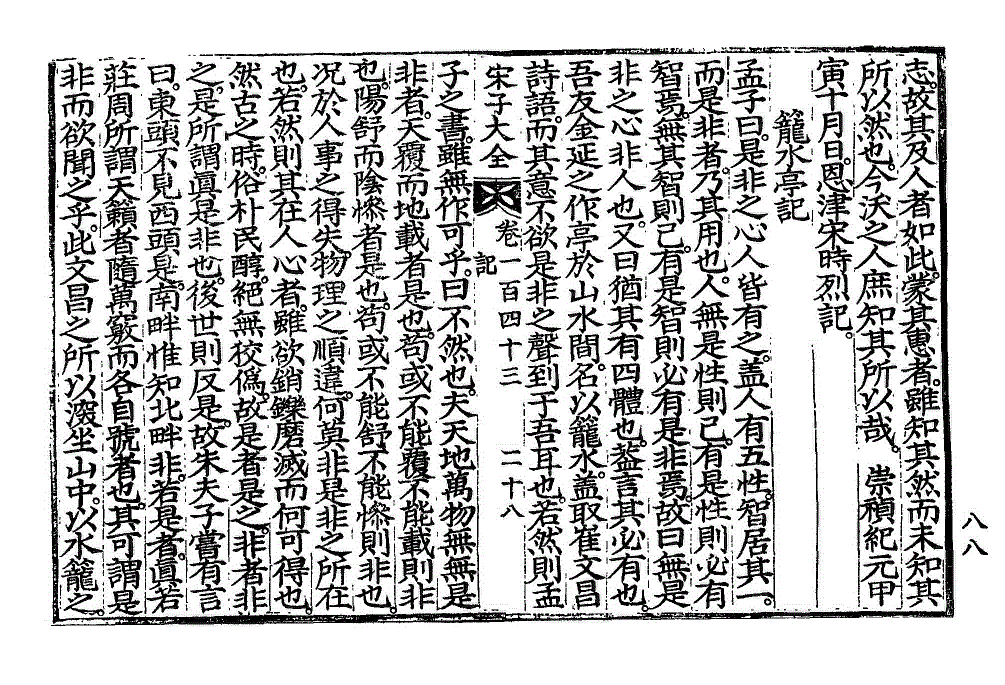 志。故其及人者如此。蒙其惠者。虽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今沃之人庶知其所以哉。 崇祯纪元甲寅十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志。故其及人者如此。蒙其惠者。虽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今沃之人庶知其所以哉。 崇祯纪元甲寅十月日。恩津宋时烈记。笼水亭记
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盖人有五性。智居其一。而是非者。乃其用也。人无是性则已。有是性则必有智焉。无其智则已。有是智则必有是非焉。故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曰犹其有四体也。盖言其必有也。吾友金延之作亭于山水间。名以笼水。盖取崔文昌诗语。而其意不欲是非之声到于吾耳也。若然则孟子之书。虽无作可乎。曰不然也。夫天地万物无无是非者。天覆而地载者是也。苟或不能覆不能载则非也。阳舒而阴惨者是也。苟或不能舒不能惨则非也。况于人事之得失。物理之顺违。何莫非是非之所在也。若然则其在人心者。虽欲销铄磨灭而何可得也。然古之时。俗朴民醇。绝无狡伪。故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是所谓真是非也。后世则反是。故朱夫子尝有言曰。东头不见西头是。南畔惟知北畔非。若是者。真若庄周所谓天籁者随万窍而各自号者也。其可谓是非而欲闻之乎。此文昌之所以深坐山中。以水笼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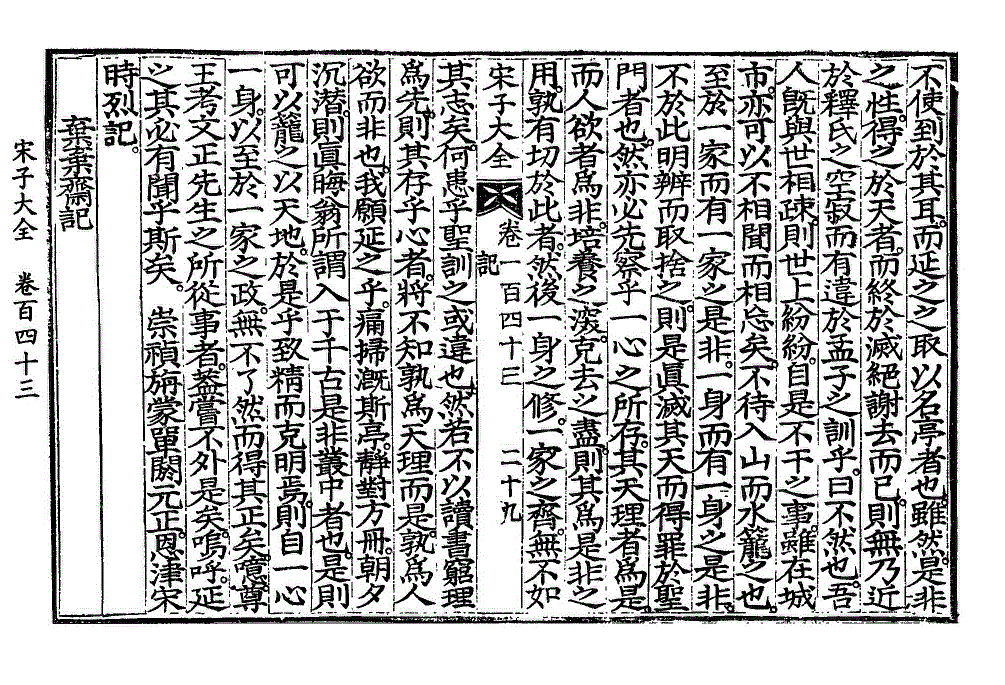 不使到于其耳。而延之之取以名亭者也。虽然。是非之性。得之于天者。而终于灭绝谢去而已。则无乃近于释氏之空寂而有违于孟子之训乎。曰不然也。吾人既与世相疏。则世上纷纷。自是不干之事。虽在城市。亦可以不相闻而相忘矣。不待入山而水笼之也。至于一家而有一家之是非。一身而有一身之是非。不于此明辨而取舍之。则是真灭其天而得罪于圣门者也。然亦必先察乎一心之所存。其天理者为是。而人欲者为非。培养之深。克去之尽。则其为是非之用。孰有切于此者。然后一身之修。一家之齐。无不如其志矣。何患乎圣训之或违也。然若不以读书穷理为先。则其存乎心者。将不知孰为天理而是。孰为人欲而非也。我愿延之乎。痛扫溉斯亭。静对方册。朝夕沈潜。则真晦翁所谓入于千古是非丛中者也。是则可以笼之以天地。于是乎致精而克明焉。则自一心一身。以至于一家之政。无不了然而得其正矣。噫。尊王考文正先生之所从事者。盖尝不外是矣。呜呼。延之其必有闻乎斯矣。 崇祯旃蒙单阏元正。恩津宋时烈记。
不使到于其耳。而延之之取以名亭者也。虽然。是非之性。得之于天者。而终于灭绝谢去而已。则无乃近于释氏之空寂而有违于孟子之训乎。曰不然也。吾人既与世相疏。则世上纷纷。自是不干之事。虽在城市。亦可以不相闻而相忘矣。不待入山而水笼之也。至于一家而有一家之是非。一身而有一身之是非。不于此明辨而取舍之。则是真灭其天而得罪于圣门者也。然亦必先察乎一心之所存。其天理者为是。而人欲者为非。培养之深。克去之尽。则其为是非之用。孰有切于此者。然后一身之修。一家之齐。无不如其志矣。何患乎圣训之或违也。然若不以读书穷理为先。则其存乎心者。将不知孰为天理而是。孰为人欲而非也。我愿延之乎。痛扫溉斯亭。静对方册。朝夕沈潜。则真晦翁所谓入于千古是非丛中者也。是则可以笼之以天地。于是乎致精而克明焉。则自一心一身。以至于一家之政。无不了然而得其正矣。噫。尊王考文正先生之所从事者。盖尝不外是矣。呜呼。延之其必有闻乎斯矣。 崇祯旃蒙单阏元正。恩津宋时烈记。弃弃斋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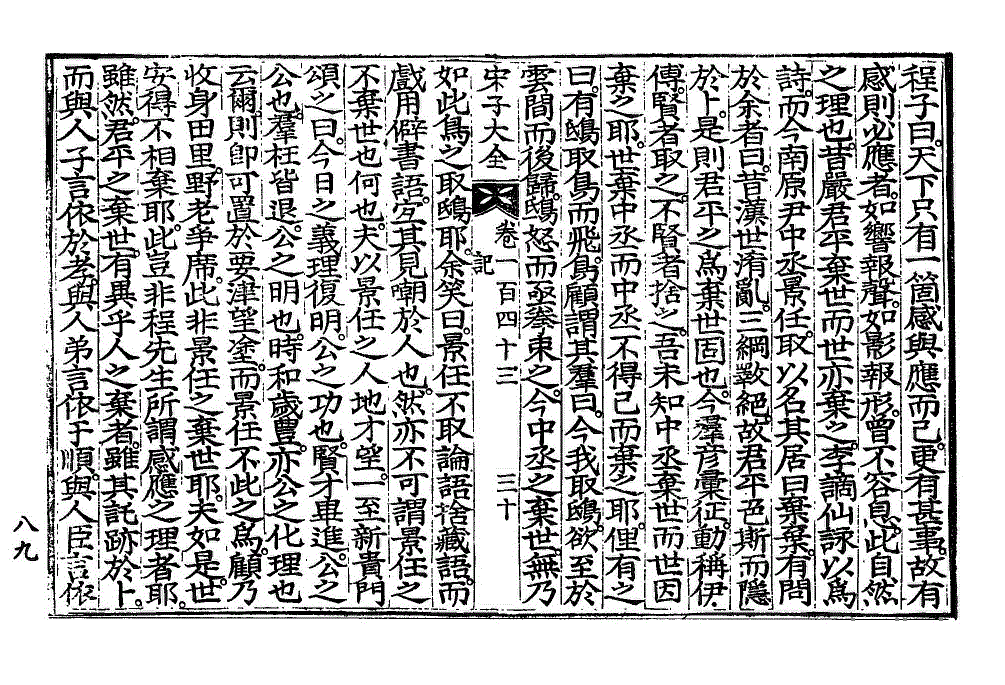 程子曰。天下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故有感则必应者。如响报声。如影报形。曾不容息。此自然之理也。昔严君平弃世而世亦弃之。李谪仙咏以为诗。而今南原尹中丞景任。取以名其居曰弃弃。有问于余者曰。昔汉世淆乱。三纲斁绝。故君平色斯而隐于卜。是则君平之为弃世固也。今群彦汇征。动称伊,傅。贤者取之。不贤者舍之。吾未知中丞弃世而世因弃之耶。世弃中丞而中丞不得已而弃之耶。俚有之曰。有鸱取鸟而飞。鸟顾谓其群曰。今我取鸱。欲至于云间而后归。鸱怒而亟拳束之。今中丞之弃世。无乃如此鸟之取鸱耶。余笑曰。景任不取论语舍藏语。而戏用僻书语。宜其见嘲于人也。然亦不可谓景任之不弃世也何也。夫以景任之人地才望。一至新贵门颂之曰。今日之义理复明。公之功也。贤才毕进。公之公也。群枉皆退。公之明也。时和岁丰。亦公之化理也云尔。则即可置于要津望涂。而景任不此之为。顾乃收身田里。野老争席。此非景任之弃世耶。夫如是。世安得不相弃耶。此岂非程先生所谓感应之理者耶。虽然。君平之弃世。有异乎人之弃者。虽其托迹于卜。而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
程子曰。天下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故有感则必应者。如响报声。如影报形。曾不容息。此自然之理也。昔严君平弃世而世亦弃之。李谪仙咏以为诗。而今南原尹中丞景任。取以名其居曰弃弃。有问于余者曰。昔汉世淆乱。三纲斁绝。故君平色斯而隐于卜。是则君平之为弃世固也。今群彦汇征。动称伊,傅。贤者取之。不贤者舍之。吾未知中丞弃世而世因弃之耶。世弃中丞而中丞不得已而弃之耶。俚有之曰。有鸱取鸟而飞。鸟顾谓其群曰。今我取鸱。欲至于云间而后归。鸱怒而亟拳束之。今中丞之弃世。无乃如此鸟之取鸱耶。余笑曰。景任不取论语舍藏语。而戏用僻书语。宜其见嘲于人也。然亦不可谓景任之不弃世也何也。夫以景任之人地才望。一至新贵门颂之曰。今日之义理复明。公之功也。贤才毕进。公之公也。群枉皆退。公之明也。时和岁丰。亦公之化理也云尔。则即可置于要津望涂。而景任不此之为。顾乃收身田里。野老争席。此非景任之弃世耶。夫如是。世安得不相弃耶。此岂非程先生所谓感应之理者耶。虽然。君平之弃世。有异乎人之弃者。虽其托迹于卜。而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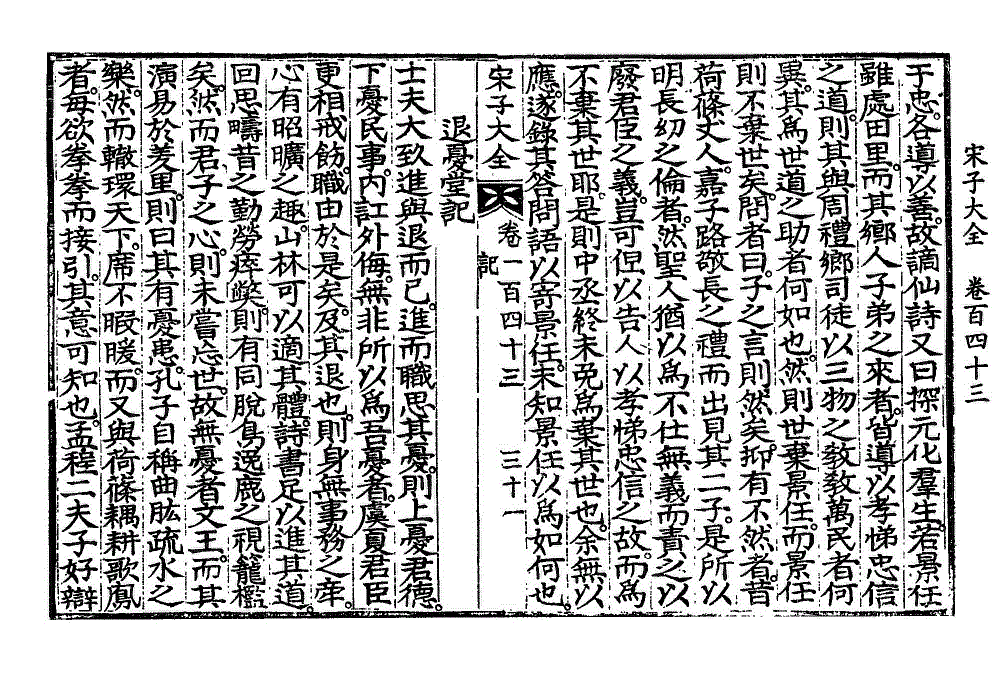 于忠。各导以善。故谪仙诗又曰探元化群生。若景任虽处田里。而其乡人子弟之来者。皆导以孝悌忠信之道。则其与周礼乡司徒以三物之教教万民者何异。其为世道之助者何如也。然则世弃景任。而景任则不弃世矣。问者曰。子之言则然矣。抑有不然者。昔荷蓧丈人。嘉子路敬长之礼而出见其二子。是所以明长幼之伦者。然圣人犹以为不仕无义而责之以废君臣之义。岂可但以告人以孝悌忠信之故。而为不弃其世耶。是则中丞终未免为弃其世也。余无以应。遂录其答问语以寄景任。未知景任以为如何也。
于忠。各导以善。故谪仙诗又曰探元化群生。若景任虽处田里。而其乡人子弟之来者。皆导以孝悌忠信之道。则其与周礼乡司徒以三物之教教万民者何异。其为世道之助者何如也。然则世弃景任。而景任则不弃世矣。问者曰。子之言则然矣。抑有不然者。昔荷蓧丈人。嘉子路敬长之礼而出见其二子。是所以明长幼之伦者。然圣人犹以为不仕无义而责之以废君臣之义。岂可但以告人以孝悌忠信之故。而为不弃其世耶。是则中丞终未免为弃其世也。余无以应。遂录其答问语以寄景任。未知景任以为如何也。退忧堂记
士夫大致进与退而已。进而职思其忧。则上忧君德。下忧民事。内讧外侮。无非所以为吾忧者。虞夏君臣更相戒饬。职由于是矣。及其退也。则身无事务之牵。心有昭旷之趣。山林可以适其体。诗书足以进其道。回思畴昔之勤劳瘁弊。则有同脱鸟逸鹿之视笼槛矣。然而君子之心。则未尝忘世。故无忧者文王。而其演易于羑里。则曰其有忧患。孔子自称曲肱疏水之乐。然而辙环天下。席不暇暖。而又与荷蓧耦耕歌凤者。每欲拳拳而接引。其意可知也。孟,程二夫子好辩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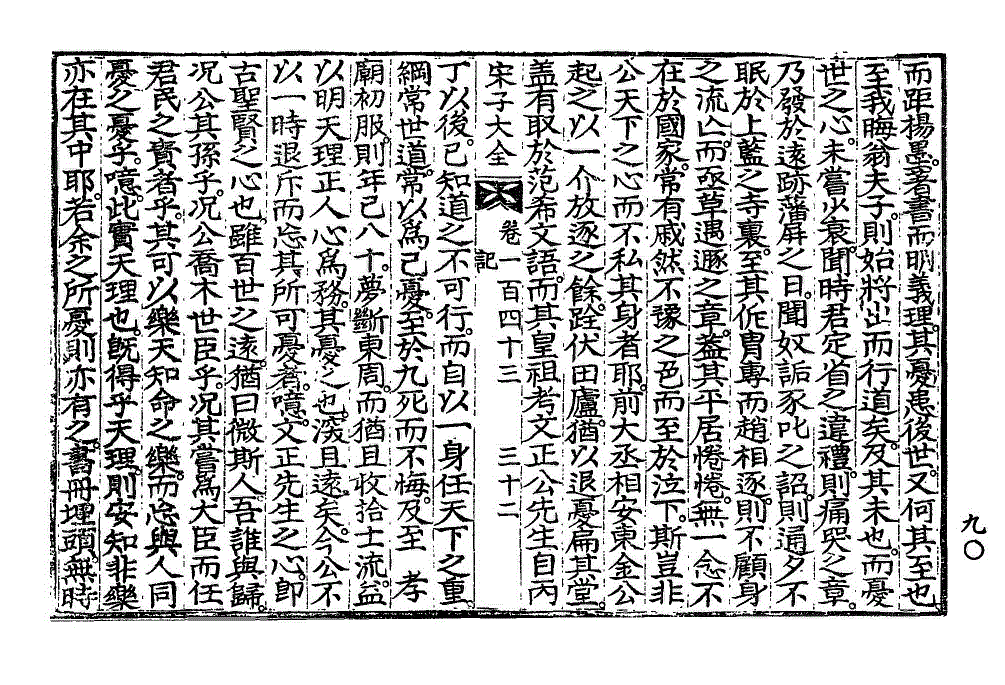 而距扬墨。著书而明义理。其忧患后世。又何其至也。至我晦翁夫子。则始将出而行道矣。及其未也。而忧世之心。未尝少衰。闻时君定省之违礼。则痛哭之章。乃发于远迹藩屏之日。闻奴诟豕叱之诏。则通夕不眠于上蓝之寺里。至其侂胄专而赵相逐。则不顾身之流亡。而亟草遇遁之章。盖其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家。常有戚然不豫之色而至于泣下。斯岂非公天下之心而不私其身者耶。前大丞相安东金公起之以一介放逐之馀。跧伏田庐。犹以退忧扁其堂。盖有取于范希文语。而其皇祖考文正公先生自丙丁以后。已知道之不可行。而自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纲常世道。常以为己忧。至于九死而不悔。及至 孝庙初服。则年已八十。梦断东周。而犹且收拾士流。益以明天理正人心为务。其忧之也。深且远矣。今公不以一时退斥而忘其所可忧者。噫。文正先生之心。即古圣贤之心也。虽百世之远。犹曰微斯人。吾谁与归。况公其孙乎。况公乔木世臣乎。况其尝为大臣而任君民之责者乎。其可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乎。噫。此实天理也。既得乎天理。则安知非乐亦在其中耶。若余之所忧则亦有之。书册埋头。无时
而距扬墨。著书而明义理。其忧患后世。又何其至也。至我晦翁夫子。则始将出而行道矣。及其未也。而忧世之心。未尝少衰。闻时君定省之违礼。则痛哭之章。乃发于远迹藩屏之日。闻奴诟豕叱之诏。则通夕不眠于上蓝之寺里。至其侂胄专而赵相逐。则不顾身之流亡。而亟草遇遁之章。盖其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家。常有戚然不豫之色而至于泣下。斯岂非公天下之心而不私其身者耶。前大丞相安东金公起之以一介放逐之馀。跧伏田庐。犹以退忧扁其堂。盖有取于范希文语。而其皇祖考文正公先生自丙丁以后。已知道之不可行。而自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纲常世道。常以为己忧。至于九死而不悔。及至 孝庙初服。则年已八十。梦断东周。而犹且收拾士流。益以明天理正人心为务。其忧之也。深且远矣。今公不以一时退斥而忘其所可忧者。噫。文正先生之心。即古圣贤之心也。虽百世之远。犹曰微斯人。吾谁与归。况公其孙乎。况公乔木世臣乎。况其尝为大臣而任君民之责者乎。其可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乎。噫。此实天理也。既得乎天理。则安知非乐亦在其中耶。若余之所忧则亦有之。书册埋头。无时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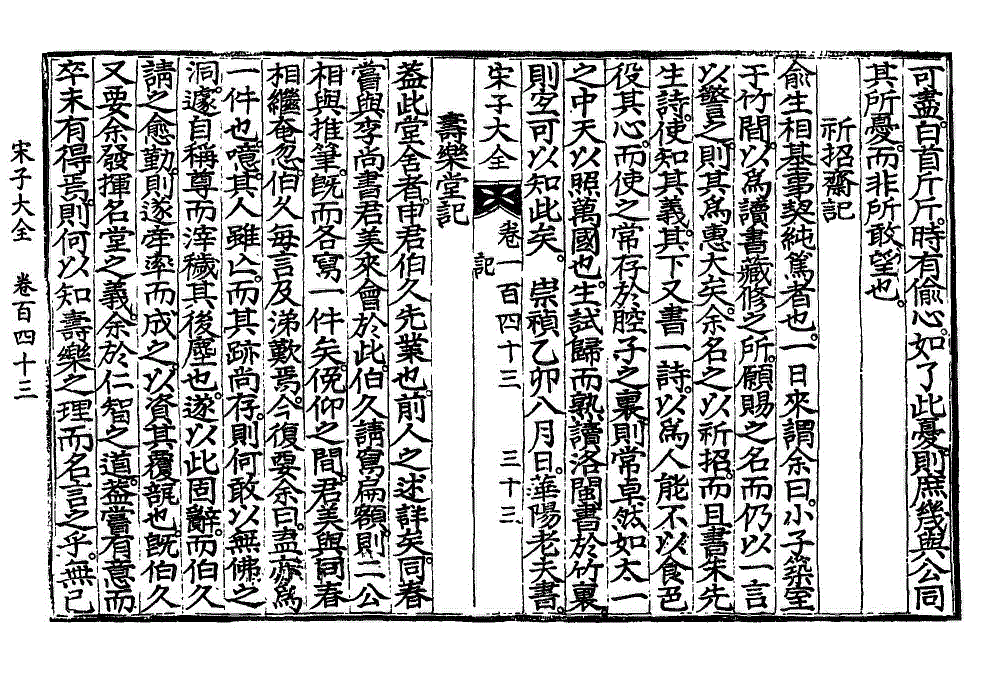 可尽。白首斤斤。时有偷心。如了此忧。则庶几与公同其所忧。而非所敢望也。
可尽。白首斤斤。时有偷心。如了此忧。则庶几与公同其所忧。而非所敢望也。祈招斋记
俞生相基事契纯笃者也。一日来谓余曰。小子筑室于竹间。以为读书藏修之所。愿赐之名而仍以一言以警之。则其为惠大矣。余名之以祈招。而且书朱先生诗。使知其义。其下又书一诗。以为人能不以食色役其心。而使之常存于腔子之里。则常卓然如太一之中天以照万国也。生试归而熟读洛闽书于竹里。则宜可以知此矣。 崇祯乙卯八月日。华阳老夫书。
寿乐堂记
盖此堂舍者。申君伯久先业也。前人之述详矣。同春尝与李尚书君美来会于此。伯久请写扁额。则二公相与推笔。既而各写一件矣。俛仰之间。君美与同春相继奄忽。伯久每言及涕叹焉。今复要余曰。盍亦为一件也。噫。其人虽亡。而其迹尚存。则何敢以无佛之洞。遽自称尊而滓秽其后尘也。遂以此固辞。而伯久请之愈勤。则遂牵率而成之。以资其覆瓿也。既伯久又要余发挥名堂之义。余于仁智之道。盖尝有意而卒未有得焉。则何以知寿乐之理而名言之乎。无已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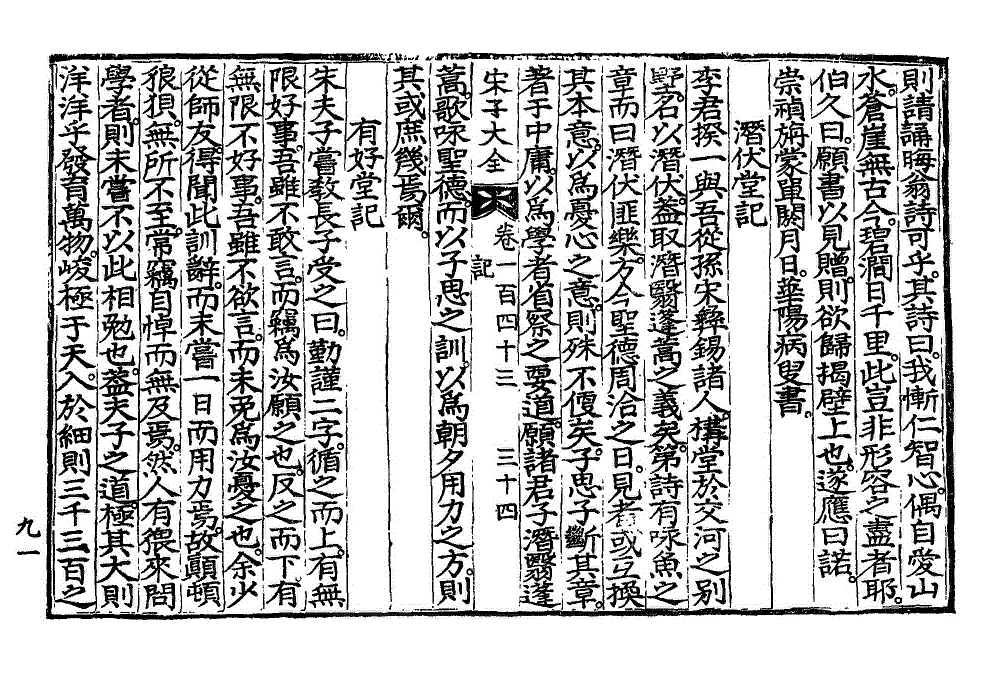 则请诵晦翁诗可乎。其诗曰。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此岂非形容之尽者耶。伯久曰。愿书以见赠。则欲归揭壁上也。遂应曰诺。 崇祯旃蒙单阏月日。华阳病叟书。
则请诵晦翁诗可乎。其诗曰。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此岂非形容之尽者耶。伯久曰。愿书以见赠。则欲归揭壁上也。遂应曰诺。 崇祯旃蒙单阏月日。华阳病叟书。潜伏堂记
李君揆一与吾从孙宋彝锡诸人。构堂于交河之别墅。名以潜伏。盖取潜翳蓬蒿之义矣。第诗有咏鱼之章而曰潜伏匪乐。方今圣德周洽之日。见者或互换其本意。以为忧心之意。则殊不便矣。子思子断其章。著于中庸。以为学者省察之要道。愿诸君子潜翳蓬蒿。歌咏圣德。而以子思之训。以为朝夕用力之方。则其或庶几焉尔。
有好堂记
朱夫子尝教长子受之曰。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虽不敢言。而窃为汝愿之也。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余少从师友。得闻此训辞。而未尝一日而用力焉。故颠顿狼狈。无所不至。常窃自悼而无及焉。然人有猥来问学者。则未尝不以此相勉也。盖夫子之道。极其大则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入于细则三千三百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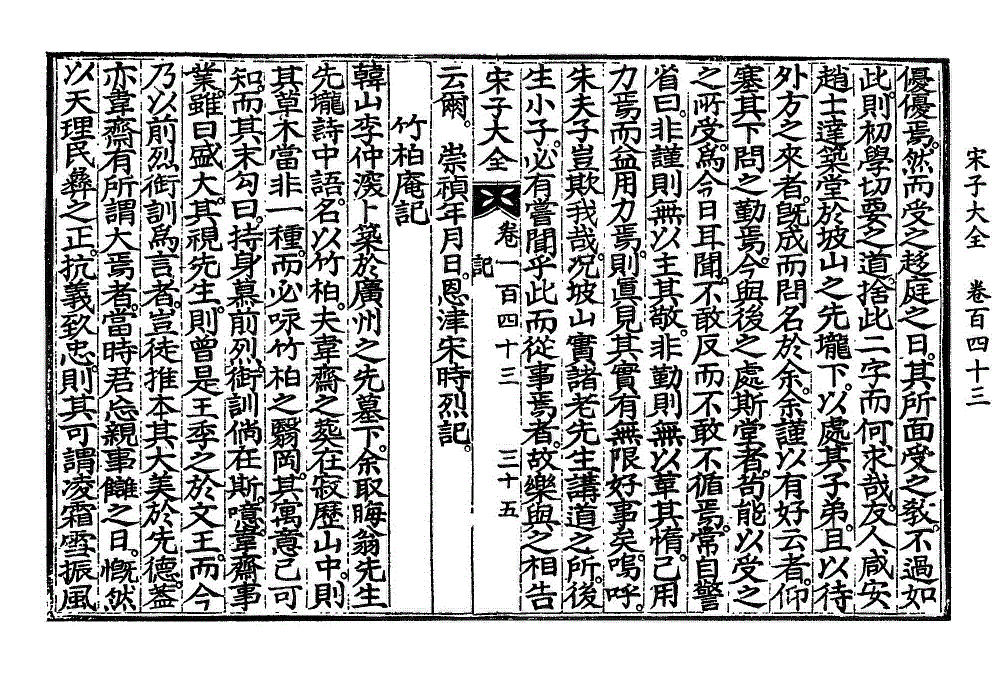 优优焉。然而受之趋庭之日。其所面受之教。不过如此。则初学切要之道。舍此二字而何求哉。友人咸安赵士达筑堂于坡山之先垄下。以处其子弟。且以待外方之来者。既成而问名于余。余谨以有好云者。仰塞其下问之勤焉。今与后之处斯堂者。苟能以受之之所受。为今日耳闻。不敢反而不敢不循焉。常自警省曰。非谨则无以主其敬。非勤则无以革其惰。已用力焉而益用力焉。则真见其实有无限好事矣。呜呼。朱夫子岂欺我哉。况坡山实诸老先生讲道之所。后生小子。必有尝闻乎此而从事焉者。故乐与之相告云尔。 崇祯年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优优焉。然而受之趋庭之日。其所面受之教。不过如此。则初学切要之道。舍此二字而何求哉。友人咸安赵士达筑堂于坡山之先垄下。以处其子弟。且以待外方之来者。既成而问名于余。余谨以有好云者。仰塞其下问之勤焉。今与后之处斯堂者。苟能以受之之所受。为今日耳闻。不敢反而不敢不循焉。常自警省曰。非谨则无以主其敬。非勤则无以革其惰。已用力焉而益用力焉。则真见其实有无限好事矣。呜呼。朱夫子岂欺我哉。况坡山实诸老先生讲道之所。后生小子。必有尝闻乎此而从事焉者。故乐与之相告云尔。 崇祯年月日。恩津宋时烈记。竹柏庵记
韩山李仲深卜筑于广州之先墓下。余取晦翁先生先垄诗中语。名以竹柏。夫韦斋之葬在寂历山中。则其草木当非一种。而必咏竹柏之翳冈。其寓意已可知。而其末句曰。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噫。韦斋事业。虽曰盛大。其视先生。则曾是王季之于文王。而今乃以前烈衔训为言者。岂徒推本其大美于先德。盖亦韦斋有所谓大焉者。当时君忘亲事雠之日。慨然以天理民彝之正。抗义致忠。则其可谓凌霜雪振风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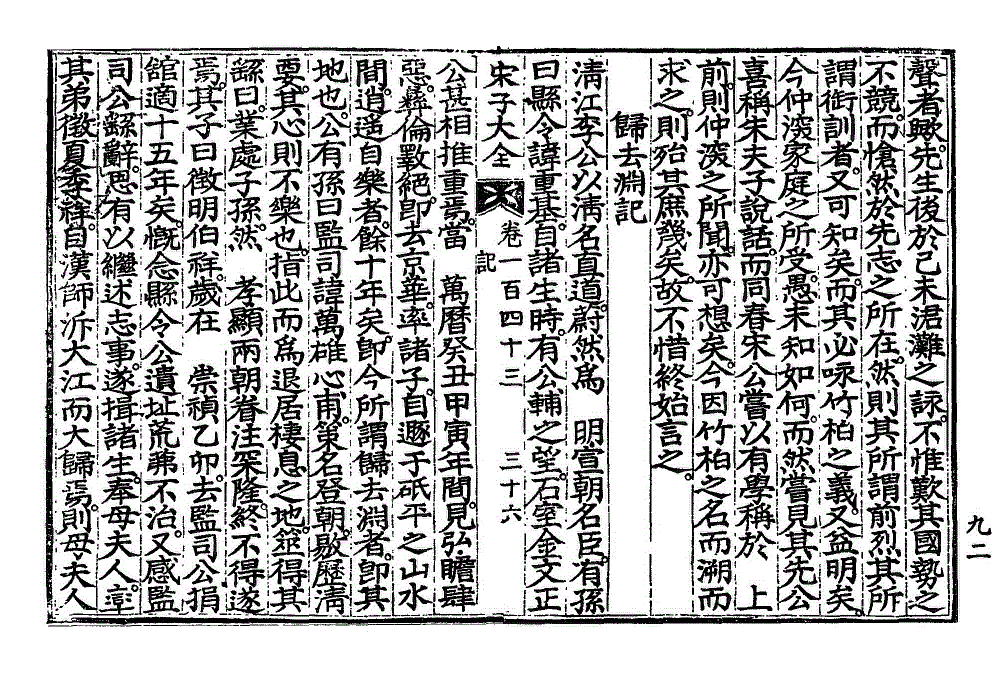 声者欤。先生后于己未涒滩之咏。不惟叹其国势之不竞。而怆然于先志之所在。然则其所谓前烈其所谓衔训者。又可知矣。而其必咏竹柏之义。又益明矣。今仲深家庭之所受。愚未知如何。而然尝见其先公喜称朱夫子说话。而同春宋公尝以有学称于 上前。则仲深之所闻。亦可想矣。今因竹柏之名而溯而求之。则殆其庶几矣。故不惜终始言之。
声者欤。先生后于己未涒滩之咏。不惟叹其国势之不竞。而怆然于先志之所在。然则其所谓前烈其所谓衔训者。又可知矣。而其必咏竹柏之义。又益明矣。今仲深家庭之所受。愚未知如何。而然尝见其先公喜称朱夫子说话。而同春宋公尝以有学称于 上前。则仲深之所闻。亦可想矣。今因竹柏之名而溯而求之。则殆其庶几矣。故不惜终始言之。归去渊记
清江李公以清名直道。蔚然为 明,宣朝名臣。有孙曰县令讳重基。自诸生时。有公辅之望。石室金文正公甚相推重焉。当 万历癸丑甲寅年间。见弘,瞻肆恶。彝伦斁绝。即去京华。率诸子。自遁于砥平之山水间。逍遥自乐者。馀十年矣。即今所谓归去渊者。即其地也。公有孙曰监司讳万雄心甫。策名登朝。扬历清要。其心则不乐也。指此而为退居栖息之地。筮得其繇曰。业处子孙。然 孝,显两朝眷注深隆。终不得遂焉。其子曰徵明伯祥。岁在 崇祯乙卯。去监司公捐馆适十五年矣。慨念县令公遗址荒茀不治。又感监司公繇辞。思有以继述志事。遂揖诸生。奉母夫人。率其弟徵夏季祥。自汉师溯大江而大归焉。则母夫人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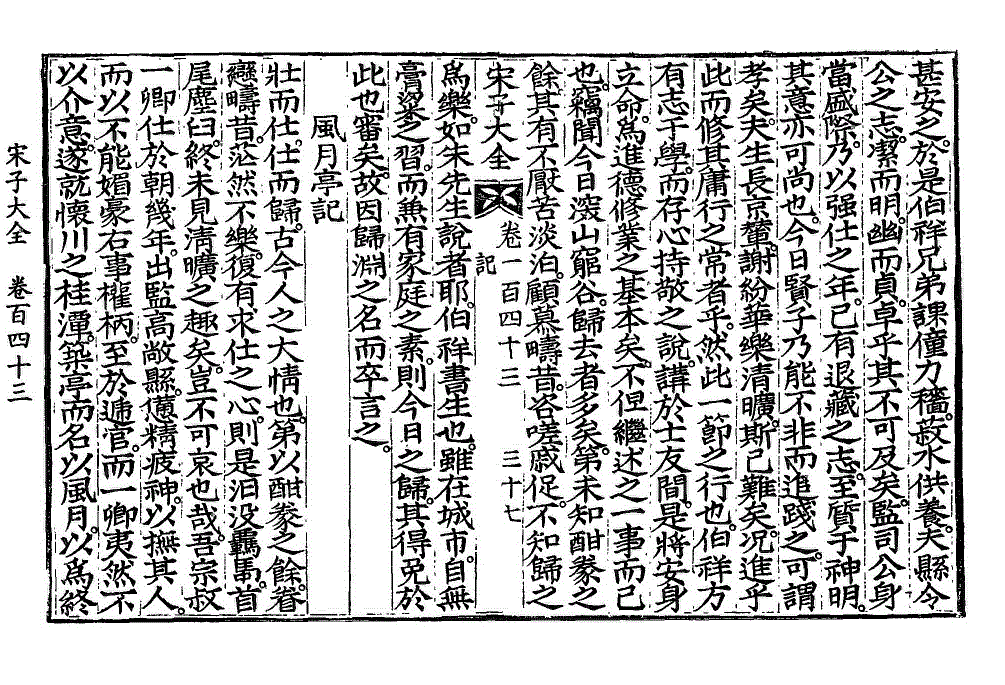 甚安之。于是伯祥兄弟课僮力穑。菽水供养。夫县令公之志。洁而明。幽而贞。卓乎其不可及矣。监司公身当盛际。乃以强仕之年。已有退藏之志。至质于神明。其意亦可尚也。今日贤子乃能不非而追践之。可谓孝矣。夫生长京辇。谢纷华乐清旷。斯已难矣。况进乎此而修其庸行之常者乎。然此一节之行也。伯祥方有志于学。而存心持敬之说。讲于士友间。是将安身立命。为进德修业之基本矣。不但继述之一事而已也。窃闻今日深山穷谷。归去者多矣。第未知酣豢之馀。其有不厌苦淡泊。顾慕畴昔。咨嗟戚促。不知归之为乐。如朱先生说者耶。伯祥书生也。虽在城市。自无膏粱之习。而兼有家庭之素。则今日之归。其得免于此也审矣。故因归渊之名而卒言之。
甚安之。于是伯祥兄弟课僮力穑。菽水供养。夫县令公之志。洁而明。幽而贞。卓乎其不可及矣。监司公身当盛际。乃以强仕之年。已有退藏之志。至质于神明。其意亦可尚也。今日贤子乃能不非而追践之。可谓孝矣。夫生长京辇。谢纷华乐清旷。斯已难矣。况进乎此而修其庸行之常者乎。然此一节之行也。伯祥方有志于学。而存心持敬之说。讲于士友间。是将安身立命。为进德修业之基本矣。不但继述之一事而已也。窃闻今日深山穷谷。归去者多矣。第未知酣豢之馀。其有不厌苦淡泊。顾慕畴昔。咨嗟戚促。不知归之为乐。如朱先生说者耶。伯祥书生也。虽在城市。自无膏粱之习。而兼有家庭之素。则今日之归。其得免于此也审矣。故因归渊之名而卒言之。风月亭记
壮而仕。仕而归。古今人之大情也。第以酣豢之馀。眷恋畴昔。茫然不乐。复有求仕之心。则是汩没羁絷。首尾尘臼。终未见清旷之趣矣。岂不可哀也哉。吾宗叔一卿仕于朝几年。出监高敞县。惫精疲神。以抚其人。而以不能媚豪右事权柄。至于递官。而一卿夷然不以介意。遂就怀川之桂潭。筑亭而名以风月。以为终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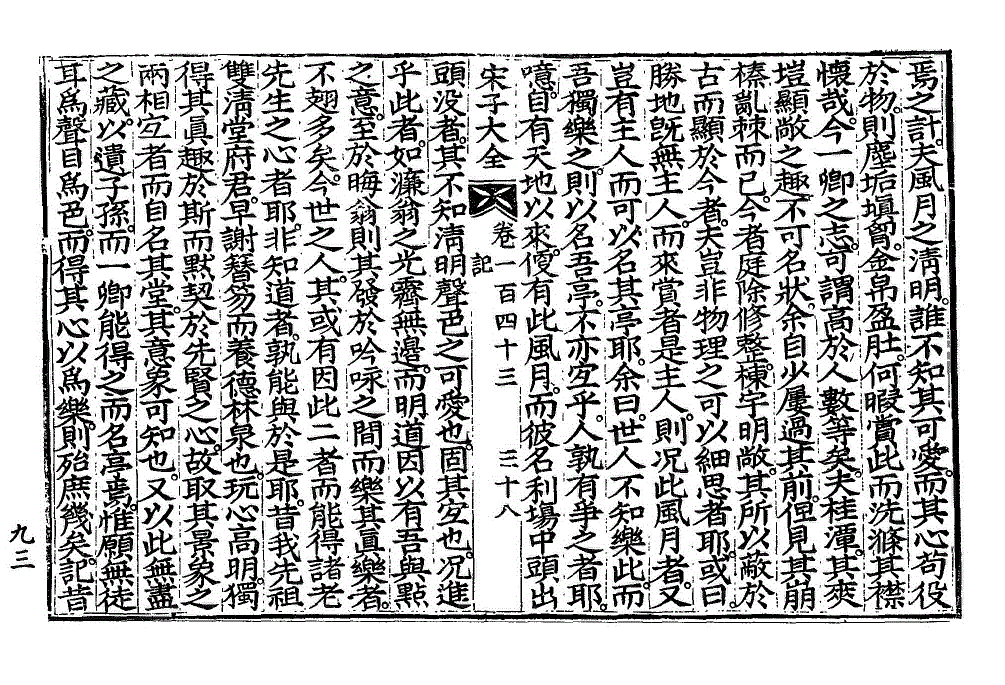 焉之计。夫风月之清明。谁不知其可爱。而其心苟役于物。则尘垢填胸。金帛盈肚。何暇赏此而洗涤其襟怀哉。今一卿之志。可谓高于人数等矣。夫桂潭。其爽垲显敞之趣。不可名状。余自少屡过其前。但见其崩榛乱棘而已。今者庭除修整。栋宇明敞。其所以蔽于古而显于今者。夫岂非物理之可以细思者耶。或曰。胜地既无主人。而来赏者是主人。则况此风月者。又岂有主人而可以名其亭耶。余曰。世人不知乐此。而吾独乐之。则以名吾亭。不亦宜乎。人孰有争之者耶。噫。自有天地以来。便有此风月。而彼名利场中头出头没者。其不知清明声色之可爱也。固其宜也。况进乎此者。如濂翁之光霁无边。而明道因以有吾与点之意。至于晦翁则其发于吟咏之间而乐其真乐者。不翅多矣。今世之人。其或有因此二者而能得诸老先生之心者耶。非知道者。孰能与于是耶。昔我先祖双清堂府君。早谢簪笏而养德林泉也。玩心高明。独得其真趣于斯而默契于先贤之心。故取其景象之两相宜者而自名其堂。其意象可知也。又以此无尽之藏。以遗子孙。而一卿能得之而名亭焉。惟愿无徒耳为声目为色。而得其心以为乐。则殆庶几矣。记昔
焉之计。夫风月之清明。谁不知其可爱。而其心苟役于物。则尘垢填胸。金帛盈肚。何暇赏此而洗涤其襟怀哉。今一卿之志。可谓高于人数等矣。夫桂潭。其爽垲显敞之趣。不可名状。余自少屡过其前。但见其崩榛乱棘而已。今者庭除修整。栋宇明敞。其所以蔽于古而显于今者。夫岂非物理之可以细思者耶。或曰。胜地既无主人。而来赏者是主人。则况此风月者。又岂有主人而可以名其亭耶。余曰。世人不知乐此。而吾独乐之。则以名吾亭。不亦宜乎。人孰有争之者耶。噫。自有天地以来。便有此风月。而彼名利场中头出头没者。其不知清明声色之可爱也。固其宜也。况进乎此者。如濂翁之光霁无边。而明道因以有吾与点之意。至于晦翁则其发于吟咏之间而乐其真乐者。不翅多矣。今世之人。其或有因此二者而能得诸老先生之心者耶。非知道者。孰能与于是耶。昔我先祖双清堂府君。早谢簪笏而养德林泉也。玩心高明。独得其真趣于斯而默契于先贤之心。故取其景象之两相宜者而自名其堂。其意象可知也。又以此无尽之藏。以遗子孙。而一卿能得之而名亭焉。惟愿无徒耳为声目为色。而得其心以为乐。则殆庶几矣。记昔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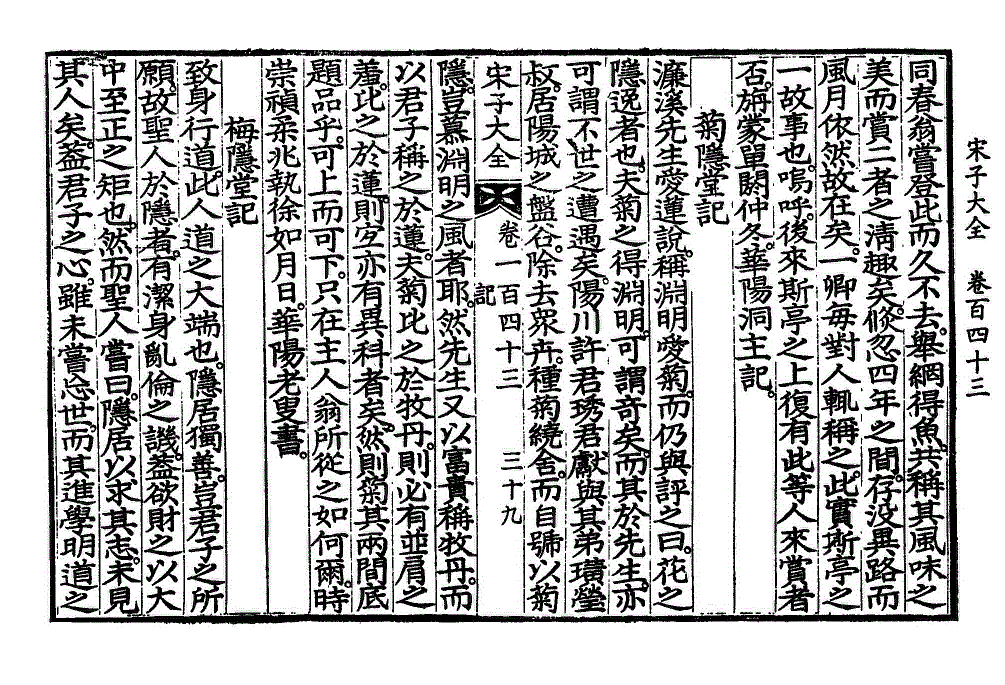 同春翁尝登此而久不去。举网得鱼。共称其风味之美而赏二者之清趣矣。倏忽四年之间。存没异路而风月依然故在矣。一卿每对人辄称之。此实斯亭之一故事也。呜呼。后来斯亭之上复有此等人来赏者否。旃蒙单阏仲冬。华阳洞主记。
同春翁尝登此而久不去。举网得鱼。共称其风味之美而赏二者之清趣矣。倏忽四年之间。存没异路而风月依然故在矣。一卿每对人辄称之。此实斯亭之一故事也。呜呼。后来斯亭之上复有此等人来赏者否。旃蒙单阏仲冬。华阳洞主记。菊隐堂记
濂溪先生爱莲说。称渊明爱菊。而仍与评之曰。花之隐逸者也。夫菊之得渊明。可谓奇矣。而其于先生。亦可谓不世之遭遇矣。阳川许君琇君献与其弟璜莹叔。居阳城之盘谷。除去众卉。种菊绕舍。而自号以菊隐。岂慕渊明之风者耶。然先生又以富贵称牧丹。而以君子称之于莲。夫菊比之于牧丹。则必有并肩之羞。比之于莲。则宜亦有异科者矣。然则菊其两间底题品乎。可上而可下。只在主人翁所从之如何尔。时崇祯柔兆执徐如月日。华阳老叟书。
梅隐堂记
致身行道。此人道之大端也。隐居独善。岂君子之所愿。故圣人于隐者。有洁身乱伦之讥。盖欲财之以大中至正之矩也。然而圣人尝曰。隐居以求其志。未见其人矣。盖君子之心。虽未尝忘世。而其进学明道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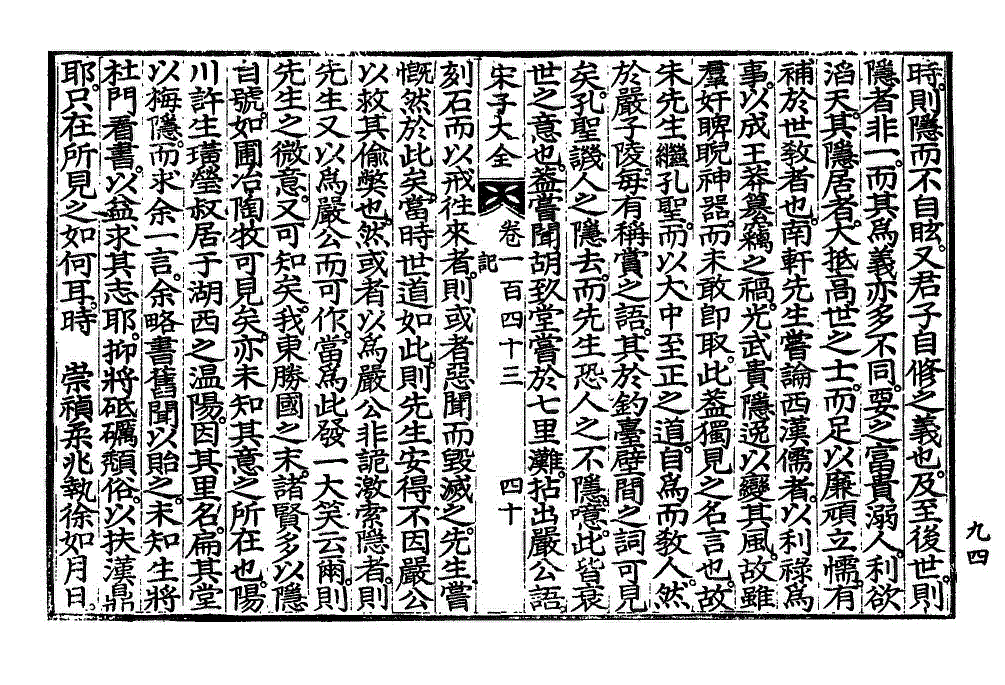 时。则隐而不自眩。又君子自修之义也。及至后世。则隐者非一。而其为义亦多不同。要之富贵溺人。利欲滔天。其隐居者。大抵高世之士。而足以廉顽立懦。有补于世教者也。南轩先生尝论西汉儒者。以利禄为事。以成王莽篡窃之祸。光武贵隐逸以变其风。故虽群奸睥睨神器。而未敢即取。此盖独见之名言也。故朱先生继孔圣。而以大中至正之道。自为而教人。然于严子陵。每有称赏之语。其于钓台壁间之词可见矣。孔圣讥人之隐去。而先生恐人之不隐。噫。此皆衰世之意也。盖尝闻胡致堂尝于七里滩。拈出严公语。刻石而以戒往来者。则或者恶闻而毁灭之。先生尝慨然于此矣。当时世道如此。则先生安得不因严公以救其偷弊也。然或者以为严公非诡激索隐者。则先生又以为严公而可作。当为此发一大笑云尔。则先生之微意。又可知矣。我东胜国之末。诸贤多以隐自号。如圃,冶,陶,牧可见矣。亦未知其意之所在也。阳川许生璜莹叔居于湖西之温阳。因其里名。扁其堂以梅隐。而求余一言。余略书旧闻以贻之。未知生将杜门看书。以益求其志耶。抑将砥砺颓俗。以扶汉鼎耶。只在所见之如何耳。时 崇祯柔兆执徐如月日。
时。则隐而不自眩。又君子自修之义也。及至后世。则隐者非一。而其为义亦多不同。要之富贵溺人。利欲滔天。其隐居者。大抵高世之士。而足以廉顽立懦。有补于世教者也。南轩先生尝论西汉儒者。以利禄为事。以成王莽篡窃之祸。光武贵隐逸以变其风。故虽群奸睥睨神器。而未敢即取。此盖独见之名言也。故朱先生继孔圣。而以大中至正之道。自为而教人。然于严子陵。每有称赏之语。其于钓台壁间之词可见矣。孔圣讥人之隐去。而先生恐人之不隐。噫。此皆衰世之意也。盖尝闻胡致堂尝于七里滩。拈出严公语。刻石而以戒往来者。则或者恶闻而毁灭之。先生尝慨然于此矣。当时世道如此。则先生安得不因严公以救其偷弊也。然或者以为严公非诡激索隐者。则先生又以为严公而可作。当为此发一大笑云尔。则先生之微意。又可知矣。我东胜国之末。诸贤多以隐自号。如圃,冶,陶,牧可见矣。亦未知其意之所在也。阳川许生璜莹叔居于湖西之温阳。因其里名。扁其堂以梅隐。而求余一言。余略书旧闻以贻之。未知生将杜门看书。以益求其志耶。抑将砥砺颓俗。以扶汉鼎耶。只在所见之如何耳。时 崇祯柔兆执徐如月日。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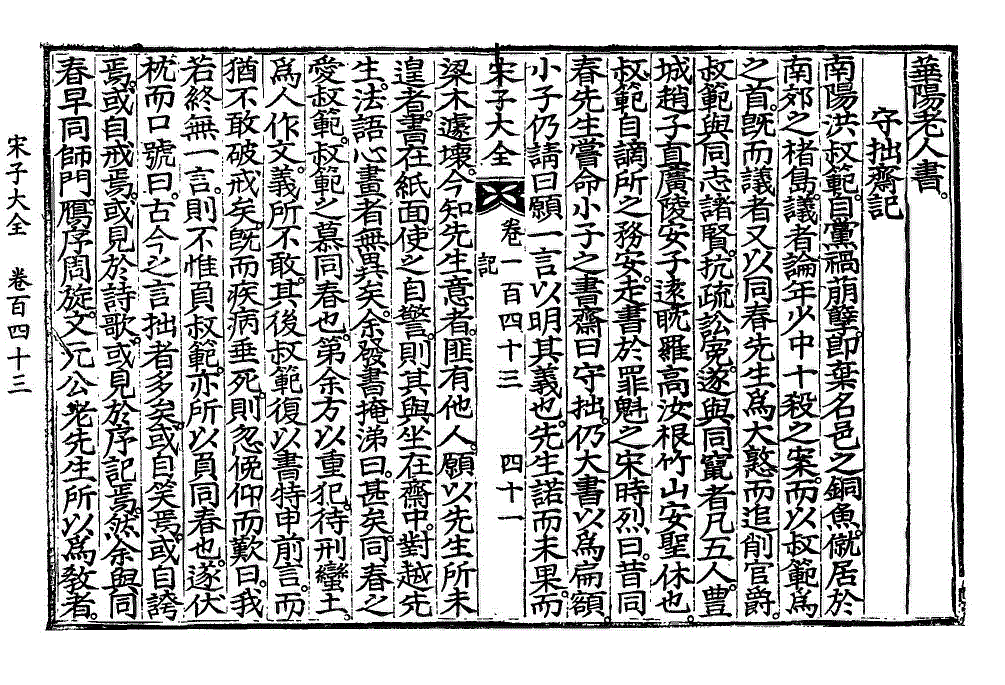 华阳老人书。
华阳老人书。守拙斋记
南阳洪叔范。自党祸萌孽。即弃名邑之铜鱼。僦居于南郊之楮岛。议者论年少中十杀之案。而以叔范为之首。既而议者又以同春先生为大憝而追削官爵。叔范与同志诸贤。抗疏讼冤。遂与同窜者凡五人。丰城赵子直,广陵安子远,耽罗高汝根,竹山安圣休也。叔范自谪所之务安。走书于罪魁之宋时烈曰。昔同春先生尝命小子之书斋曰守拙。仍大书以为扁额。小子仍请曰愿一言以明其义也。先生诺而未果。而梁木遽坏。今知先生意者。匪有他人。愿以先生所未遑者。书在纸面。使之自警。则其与坐在斋中。对越先生。法语心画者无异矣。余发书掩涕曰。甚矣。同春之爱叔范。叔范之慕同春也。第余方以重犯。待刑蛮土。为人作文。义所不敢。其后叔范复以书特申前言。而犹不敢破戒矣。既而疾病垂死。则忽俛仰而叹曰。我若终无一言。则不惟负叔范。亦所以负同春也。遂伏枕而口号曰。古今之言拙者多矣。或自笑焉。或自誇焉。或自戒焉。或见于诗歌。或见于序记焉。然余与同春早同师门。雁序周旋。文元公老先生所以为教者。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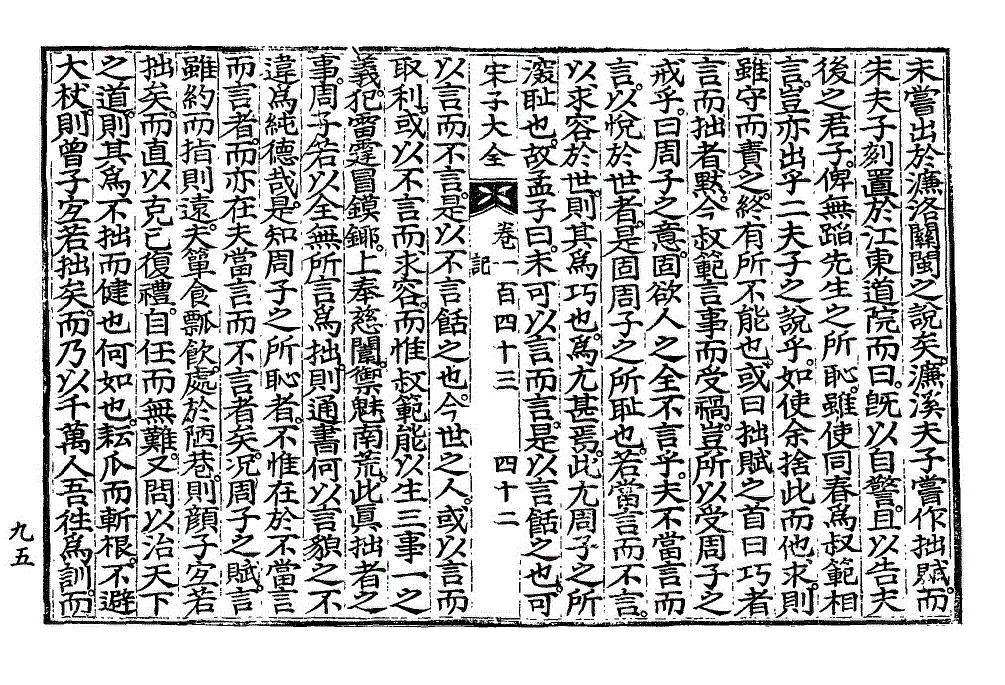 未尝出于濂洛关闽之说矣。濂溪夫子尝作拙赋。而朱夫子刻置于江东道院而曰。既以自警。且以告夫后之君子。俾无蹈先生之所耻。虽使同春为叔范相言。岂亦出乎二夫子之说乎。如使余舍此而他求。则虽守而责之。终有所不能也。或曰拙赋之首曰巧者言而拙者默。今叔范言事而受祸。岂所以受周子之戒乎。曰周子之意。固欲人之全不言乎。夫不当言而言。以悦于世者。是固周子之所耻也。若当言而不言。以求容于世。则其为巧也。为尤甚焉。此尤周子之所深耻也。故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今世之人。或以言而取利。或以不言而求容。而惟叔范能以生三事一之义。犯雷霆冒镆铘。上奉慈闱。御魅南荒。此真拙者之事。周子若以全无所言为拙。则通书何以言貌之不违为纯德哉。是知周子之所耻者。不惟在于不当言而言者。而亦在夫当言而不言者矣。况周子之赋。言虽约而指则远。夫箪食瓢饮。处于陋巷。则颜子宜若拙矣。而直以克己复礼。自任而无难。又问以治天下之道。则其为不拙而健也何如也。耘瓜而斩根。不避大杖。则曾子宜若拙矣。而乃以千万人吾往为训。而
未尝出于濂洛关闽之说矣。濂溪夫子尝作拙赋。而朱夫子刻置于江东道院而曰。既以自警。且以告夫后之君子。俾无蹈先生之所耻。虽使同春为叔范相言。岂亦出乎二夫子之说乎。如使余舍此而他求。则虽守而责之。终有所不能也。或曰拙赋之首曰巧者言而拙者默。今叔范言事而受祸。岂所以受周子之戒乎。曰周子之意。固欲人之全不言乎。夫不当言而言。以悦于世者。是固周子之所耻也。若当言而不言。以求容于世。则其为巧也。为尤甚焉。此尤周子之所深耻也。故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今世之人。或以言而取利。或以不言而求容。而惟叔范能以生三事一之义。犯雷霆冒镆铘。上奉慈闱。御魅南荒。此真拙者之事。周子若以全无所言为拙。则通书何以言貌之不违为纯德哉。是知周子之所耻者。不惟在于不当言而言者。而亦在夫当言而不言者矣。况周子之赋。言虽约而指则远。夫箪食瓢饮。处于陋巷。则颜子宜若拙矣。而直以克己复礼。自任而无难。又问以治天下之道。则其为不拙而健也何如也。耘瓜而斩根。不避大杖。则曾子宜若拙矣。而乃以千万人吾往为训。而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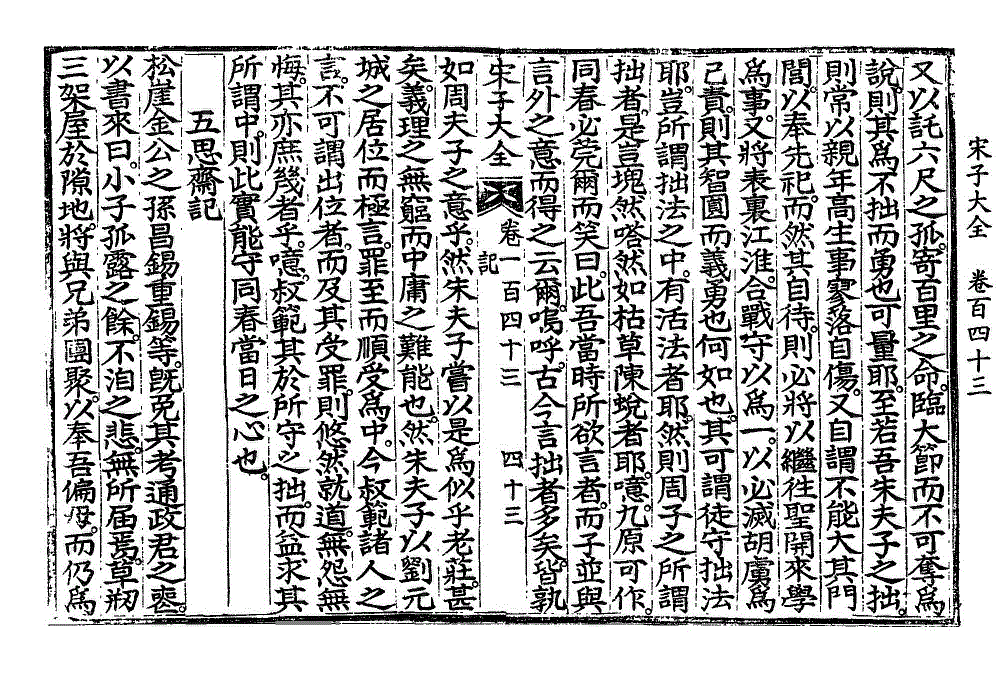 又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为说。则其为不拙而勇也可量耶。至若吾朱夫子之拙。则常以亲年高生事寥落自伤。又自谓不能大其门闾。以奉先祀。而然其自待。则必将以继往圣开来学为事。又将表里江淮。合战守以为一。以必灭胡虏为己责。则其智圆而义勇也何如也。其可谓徒守拙法耶。岂所谓拙法之中。有活法者耶。然则周子之所谓拙者。是岂块然嗒然如枯草陈蜕者耶。噫。九原可作。同春必莞尔而笑曰。此吾当时所欲言者。而子并与言外之意而得之云尔。呜呼。古今言拙者多矣。皆孰如周夫子之意乎。然朱夫子尝以是为似乎老庄。甚矣。义理之无穷而中庸之难能也。然朱夫子以刘元城之居位而极言。罪至而顺受为中。今叔范诸人之言。不可谓出位者。而及其受罪。则悠然就道。无怨无悔。其亦庶几者乎。噫。叔范其于所守之拙。而益求其所谓中。则此实能守同春当日之心也。
又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为说。则其为不拙而勇也可量耶。至若吾朱夫子之拙。则常以亲年高生事寥落自伤。又自谓不能大其门闾。以奉先祀。而然其自待。则必将以继往圣开来学为事。又将表里江淮。合战守以为一。以必灭胡虏为己责。则其智圆而义勇也何如也。其可谓徒守拙法耶。岂所谓拙法之中。有活法者耶。然则周子之所谓拙者。是岂块然嗒然如枯草陈蜕者耶。噫。九原可作。同春必莞尔而笑曰。此吾当时所欲言者。而子并与言外之意而得之云尔。呜呼。古今言拙者多矣。皆孰如周夫子之意乎。然朱夫子尝以是为似乎老庄。甚矣。义理之无穷而中庸之难能也。然朱夫子以刘元城之居位而极言。罪至而顺受为中。今叔范诸人之言。不可谓出位者。而及其受罪。则悠然就道。无怨无悔。其亦庶几者乎。噫。叔范其于所守之拙。而益求其所谓中。则此实能守同春当日之心也。五思斋记
松崖金公之孙昌锡,重锡等。既免其考通政君之丧。以书来曰。小子孤露之馀。不洎之悲。无所届焉。草刱三架屋于隙地。将与兄弟团聚。以奉吾偏母。而仍为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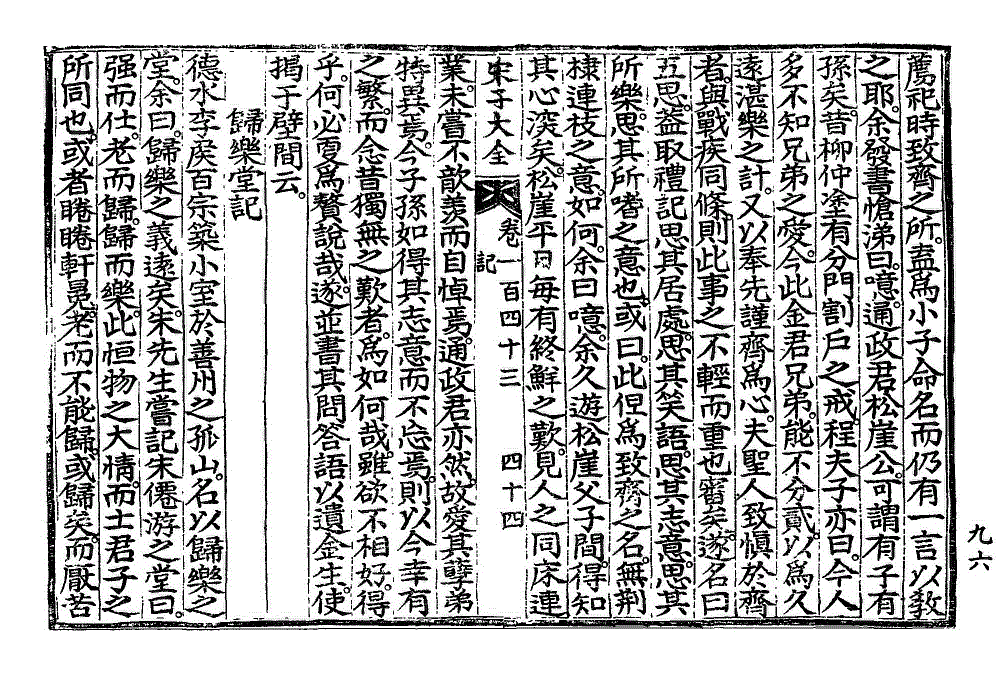 荐祀时致齐之所。盍为小子命名而仍有一言以教之耶。余发书怆涕曰。噫。通政君,松崖公。可谓有子有孙矣。昔柳仲涂有分门割户之戒。程夫子亦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今此金君兄弟。能不分贰。以为久远湛乐之计。又以奉先谨齐为心。夫圣人致慎于齐者。与战疾同条。则此事之不轻而重也审矣。遂名曰五思。盖取礼记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之意也。或曰。此但为致齐之名。无荆棣连枝之意。如何。余曰噫。余久游松崖父子间。得知其心深矣。松崖平日每有终鲜之叹。见人之同床连业。未尝不歆羡而自悼焉。通政君亦然。故爱其孽弟特异焉。今子孙如得其志意而不忘焉。则以今幸有之繁。而念昔独无之叹者。为如何哉。虽欲不相好。得乎。何必更为赘说哉。遂并书其问答语以遗金生。使揭于壁间云。
荐祀时致齐之所。盍为小子命名而仍有一言以教之耶。余发书怆涕曰。噫。通政君,松崖公。可谓有子有孙矣。昔柳仲涂有分门割户之戒。程夫子亦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今此金君兄弟。能不分贰。以为久远湛乐之计。又以奉先谨齐为心。夫圣人致慎于齐者。与战疾同条。则此事之不轻而重也审矣。遂名曰五思。盖取礼记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之意也。或曰。此但为致齐之名。无荆棣连枝之意。如何。余曰噫。余久游松崖父子间。得知其心深矣。松崖平日每有终鲜之叹。见人之同床连业。未尝不歆羡而自悼焉。通政君亦然。故爱其孽弟特异焉。今子孙如得其志意而不忘焉。则以今幸有之繁。而念昔独无之叹者。为如何哉。虽欲不相好。得乎。何必更为赘说哉。遂并书其问答语以遗金生。使揭于壁间云。归乐堂记
德水李侯百宗筑小室于善州之孤山。名以归乐之堂。余曰。归乐之义远矣。朱先生尝记朱仙游之堂曰。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恒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或者眷眷轩冕。老而不能归。或归矣。而厌苦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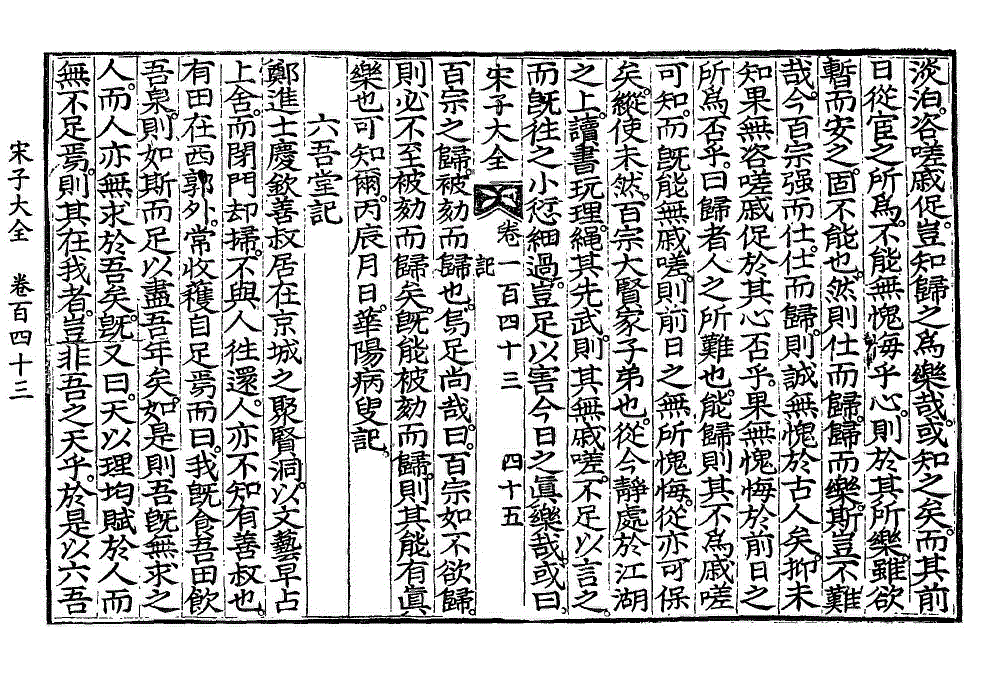 淡泊。咨嗟戚促。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其前日从宦之所为。不能无愧悔乎心。则于其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固不能也。然则仕而归。归而乐。斯岂不难哉。今百宗强而仕。仕而归。则诚无愧于古人矣。抑未知果无咨嗟戚促于其心否乎。果无愧悔于前日之所为否乎。曰归者。人之所难也。能归则其不为戚嗟可知。而既能无戚嗟。则前日之无所愧悔。从亦可保矣。纵使未然。百宗大贤家子弟也。从今静处于江湖之上。读书玩理。绳其先武。则其无戚嗟。不足以言之。而既往之小愆细过。岂足以害今日之真乐哉。或曰。百宗之归。被劾而归也。乌足尚哉。曰。百宗如不欲归。则必不至被劾而归矣。既能被劾而归。则其能有真乐也可知尔。丙辰月日。华阳病叟记。
淡泊。咨嗟戚促。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其前日从宦之所为。不能无愧悔乎心。则于其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固不能也。然则仕而归。归而乐。斯岂不难哉。今百宗强而仕。仕而归。则诚无愧于古人矣。抑未知果无咨嗟戚促于其心否乎。果无愧悔于前日之所为否乎。曰归者。人之所难也。能归则其不为戚嗟可知。而既能无戚嗟。则前日之无所愧悔。从亦可保矣。纵使未然。百宗大贤家子弟也。从今静处于江湖之上。读书玩理。绳其先武。则其无戚嗟。不足以言之。而既往之小愆细过。岂足以害今日之真乐哉。或曰。百宗之归。被劾而归也。乌足尚哉。曰。百宗如不欲归。则必不至被劾而归矣。既能被劾而归。则其能有真乐也可知尔。丙辰月日。华阳病叟记。六吾堂记
郑进士庆钦善叔居在京城之聚贤洞。以文艺早占上舍。而闭门却扫。不与人往还。人亦不知有善叔也。有田在西郭外。常收穫自足焉而曰。我既食吾田饮吾泉。则如斯而足以尽吾年矣。如是则吾既无求之人。而人亦无求于吾矣。既又曰。天以理均赋于人而无不足焉。则其在我者。岂非吾之天乎。于是以六吾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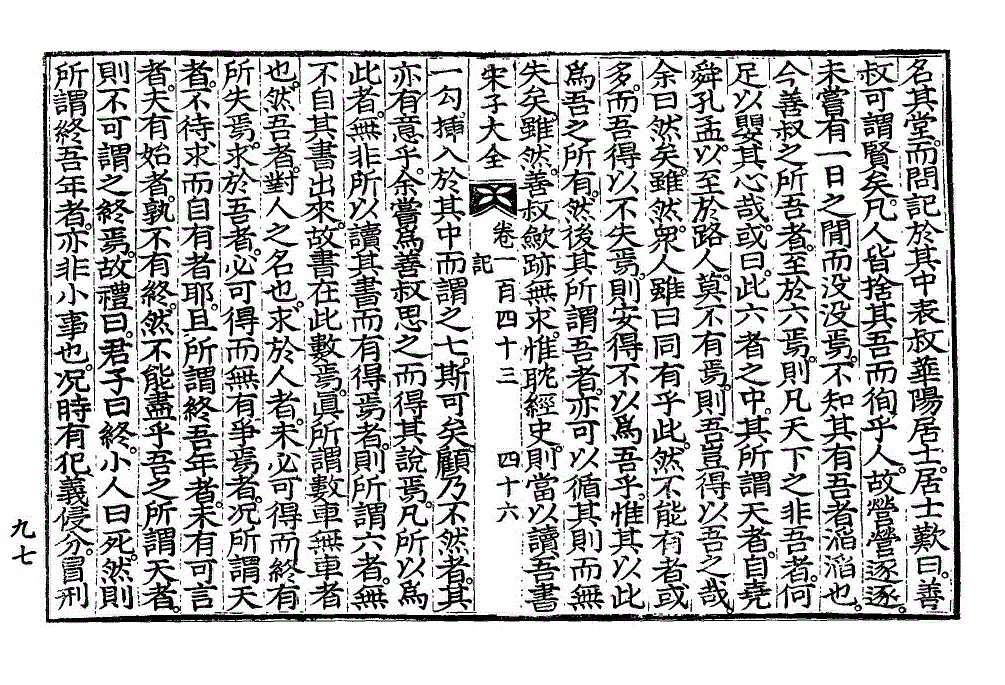 名其堂。而问记于其中表叔华阳居士。居士叹曰。善叔可谓贤矣。凡人皆舍其吾而徇乎人。故营营逐逐。未尝有一日之閒而没没焉。不知其有吾者滔滔也。今善叔之所吾者。至于六焉。则凡天下之非吾者。何足以婴其心哉。或曰。此六者之中。其所谓天者。自尧舜,孔孟。以至于路人。莫不有焉。则吾岂得以吾之哉。余曰然矣。虽然。众人虽曰同有乎此。然不能有者或多。而吾得以不失焉。则安得不以为吾乎。惟其以此为吾之所有。然后其所谓吾者。亦可以循其则而无失矣。虽然。善叔敛迹无求。惟耽经史。则当以读吾书一句。插入于其中而谓之七。斯可矣。顾乃不然者。其亦有意乎。余尝为善叔思之而得其说焉。凡所以为此者。无非所以读其书而有得焉者。则所谓六者。无不自其书出来。故书在此数焉。真所谓数车无车者也。然吾者。对人之名也。求于人者。未必可得而终有所失焉。求于吾者。必可得而无有争焉者。况所谓天者。不待求而自有者耶。且所谓终吾年者。未有可言者。夫有始者。孰不有终。然不能尽乎吾之所谓天者。则不可谓之终焉。故礼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然则所谓终吾年者。亦非小事也。况时有犯义侵分。冒刑
名其堂。而问记于其中表叔华阳居士。居士叹曰。善叔可谓贤矣。凡人皆舍其吾而徇乎人。故营营逐逐。未尝有一日之閒而没没焉。不知其有吾者滔滔也。今善叔之所吾者。至于六焉。则凡天下之非吾者。何足以婴其心哉。或曰。此六者之中。其所谓天者。自尧舜,孔孟。以至于路人。莫不有焉。则吾岂得以吾之哉。余曰然矣。虽然。众人虽曰同有乎此。然不能有者或多。而吾得以不失焉。则安得不以为吾乎。惟其以此为吾之所有。然后其所谓吾者。亦可以循其则而无失矣。虽然。善叔敛迹无求。惟耽经史。则当以读吾书一句。插入于其中而谓之七。斯可矣。顾乃不然者。其亦有意乎。余尝为善叔思之而得其说焉。凡所以为此者。无非所以读其书而有得焉者。则所谓六者。无不自其书出来。故书在此数焉。真所谓数车无车者也。然吾者。对人之名也。求于人者。未必可得而终有所失焉。求于吾者。必可得而无有争焉者。况所谓天者。不待求而自有者耶。且所谓终吾年者。未有可言者。夫有始者。孰不有终。然不能尽乎吾之所谓天者。则不可谓之终焉。故礼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然则所谓终吾年者。亦非小事也。况时有犯义侵分。冒刑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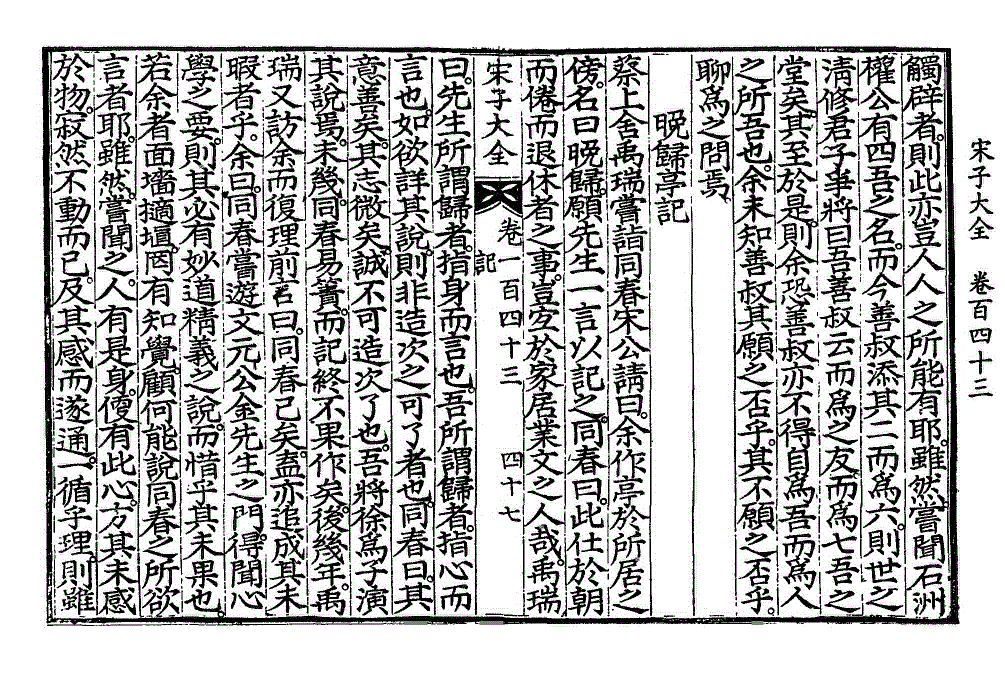 触辟者。则此亦岂人人之所能有耶。虽然。尝闻石洲权公有四吾之名。而今善叔添其二而为六。则世之清修君子争将曰吾善叔云而为之友。而为七吾之堂矣。其至于是。则余恐善叔亦不得自为吾而为人之所吾也。余未知善叔其愿之否乎。其不愿之否乎。聊为之问焉。
触辟者。则此亦岂人人之所能有耶。虽然。尝闻石洲权公有四吾之名。而今善叔添其二而为六。则世之清修君子争将曰吾善叔云而为之友。而为七吾之堂矣。其至于是。则余恐善叔亦不得自为吾而为人之所吾也。余未知善叔其愿之否乎。其不愿之否乎。聊为之问焉。晚归亭记
蔡上舍禹瑞尝诣同春宋公请曰。余作亭于所居之傍。名曰晚归。愿先生一言以记之。同春曰。此仕于朝而倦而退休者之事。岂宜于家居业文之人哉。禹瑞曰。先生所谓归者。指身而言也。吾所谓归者。指心而言也。如欲详其说。则非造次之可了者也。同春曰。其意善矣。其志微矣。诚不可造次了也。吾将徐为子演其说焉。未几。同春易箦。而记终不果作矣。后几年。禹瑞又访余而复理前言曰。同春已矣。盍亦追成其未暇者乎。余曰。同春尝游文元公金先生之门。得闻心学之要。则其必有妙道精义之说。而惜乎其未果也。若余者面墙擿埴。罔有知觉。顾何能说同春之所欲言者耶。虽然。尝闻之。人有是身。便有此心。方其未感于物。寂然不动而已。及其感而遂通。一循乎理。则虽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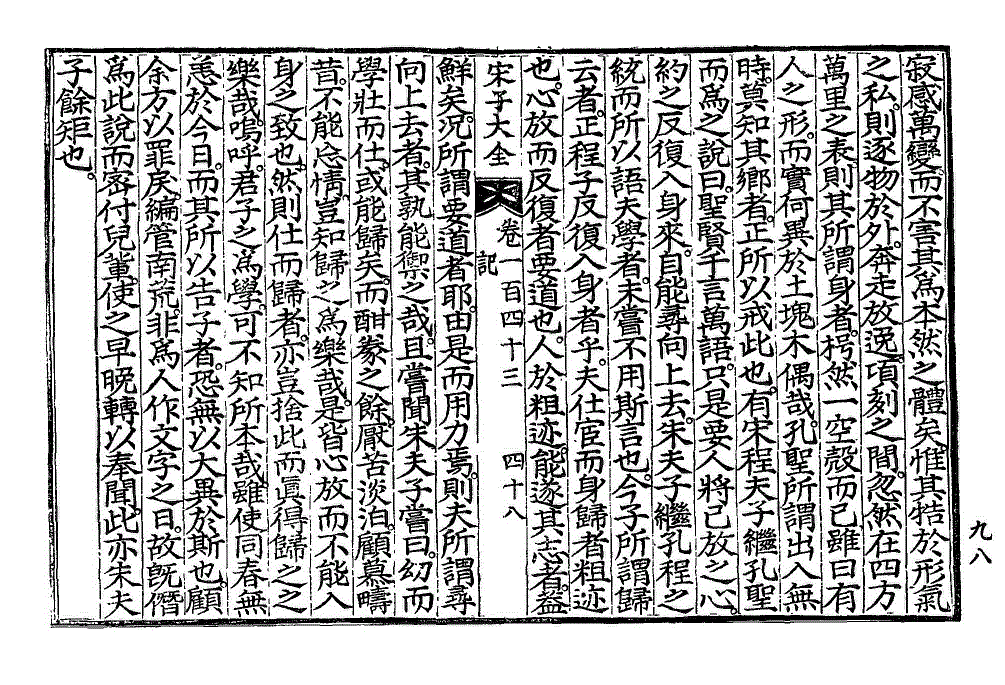 寂感万变。而不害其为本然之体矣。惟其牿于形气之私。则逐物于外。奔走放逸。顷刻之间。忽然在四方万里之表。则其所谓身者。枵然一空壳而已。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异于土块木偶哉。孔圣所谓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正所以戒此也。有宋程夫子继孔圣而为之说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将已放之心。约之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朱夫子继孔程之统而所以语夫学者。未尝不用斯言也。今子所谓归云者。正程子反复入身者乎。夫仕宦而身归者粗迹也。心放而反复者要道也。人于粗迹。能遂其志者。盖鲜矣。况所谓要道者耶。由是而用力焉。则夫所谓寻向上去者。其孰能御之哉。且尝闻朱夫子尝曰。幼而学壮而仕。或能归矣。而酣豢之馀。厌苦淡泊。顾慕畴昔。不能忘情。岂知归之为乐哉。是皆心放而不能入身之致也。然则仕而归者。亦岂舍此而真得归之之乐哉。呜呼。君子之为学。可不知所本哉。虽使同春无恙于今日。而其所以告子者。恐无以大异于斯也。顾余方以罪戾。编管南荒。非为人作文字之日。故既僭为此说而密付儿辈。使之早晚转以奉闻。此亦朱夫子馀矩也。
寂感万变。而不害其为本然之体矣。惟其牿于形气之私。则逐物于外。奔走放逸。顷刻之间。忽然在四方万里之表。则其所谓身者。枵然一空壳而已。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异于土块木偶哉。孔圣所谓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正所以戒此也。有宋程夫子继孔圣而为之说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将已放之心。约之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朱夫子继孔程之统而所以语夫学者。未尝不用斯言也。今子所谓归云者。正程子反复入身者乎。夫仕宦而身归者粗迹也。心放而反复者要道也。人于粗迹。能遂其志者。盖鲜矣。况所谓要道者耶。由是而用力焉。则夫所谓寻向上去者。其孰能御之哉。且尝闻朱夫子尝曰。幼而学壮而仕。或能归矣。而酣豢之馀。厌苦淡泊。顾慕畴昔。不能忘情。岂知归之为乐哉。是皆心放而不能入身之致也。然则仕而归者。亦岂舍此而真得归之之乐哉。呜呼。君子之为学。可不知所本哉。虽使同春无恙于今日。而其所以告子者。恐无以大异于斯也。顾余方以罪戾。编管南荒。非为人作文字之日。故既僭为此说而密付儿辈。使之早晚转以奉闻。此亦朱夫子馀矩也。隐求窝记
李生子元始居畿辅。自乙卯挈家至岭东之海滨。力田以自给。今者艰关数十日程。访余于蓬岛。因请曰。小子略构小屋于所寓。将有终焉之计。盍赐之名。余书以隐求而语之曰。生去桑梓离亲朋。为耕云钓月之事。彷佛于隐者貌样也。决性命之正。以饕富贵。既非所虑。而与鸟兽同群。又非依中庸之意。惟读书求志。则庶几乎遁世无闷之万一。而山前荷篑之知。亦不须怕也。生曰。敢不服膺。余遂书其说以送其行。丙辰至月日。蓬山人。
联棣堂记
恭惟我世德。旧以孝友相传。西阜府君至性纯笃。当圭庵先生谪居泗川也。每祷于日月。冀其亟蒙宥还。及其宥还。不胜悲喜。遂感疾而没。至我叔父习静公。又与我先府君睡翁公。皆寓居于永同,沃川之境。相去十许里。逐逐往还。三日为疏。酒熟则相就。味美则相须。率不待蹄涔之渴而辄必会。会必两忘其所趋。犹以不得同居为恨。及习静公摈斥北邮也。寄诗曰。雁向湖西阔。人羁塞北幽。先府君吟咏凝泪。常揭壁寓目。如见颜面焉。及习静公没于关西。先府君当流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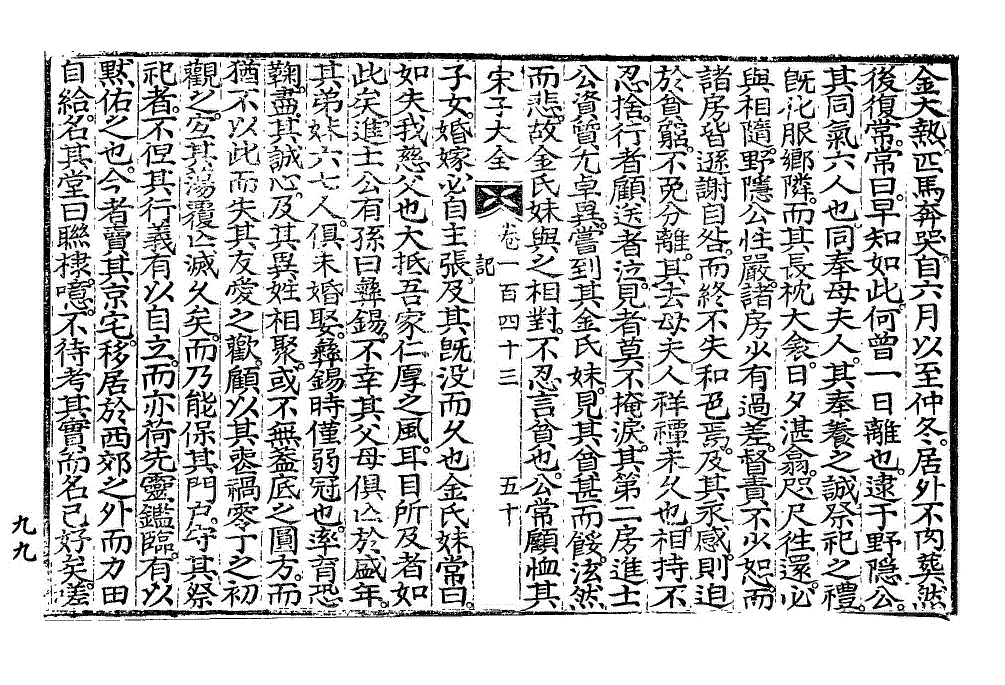 金大热。匹马奔哭。自六月以至仲冬。居外不肉葬然后复常。常曰。早知如此。何曾一日离也。逮于野隐公。其同气六人也。同奉母夫人。其奉养之诚。祭祀之礼。既化服乡邻。而其长枕大衾。日夕湛翕。咫尺往还。必与相随。野隐公性严。诸房少有过差。督责不少恕。而诸房皆逊谢自咎。而终不失和色焉。及其永感。则迫于贫穷。不免分离。其去母夫人祥禫未久也。相持不忍舍。行者顾送者泣。见者莫不掩泪。其第二房进士公资质尤卓异。尝到其金氏妹。见其贫甚而馁。泫然而悲。故金氏妹与之相对。不忍言贫也。公常顾恤其子女。婚嫁必自主张。及其既没而久也。金氏妹常曰。如失我慈父也。大抵吾家仁厚之风。耳目所及者如此矣。进士公有孙曰彝锡。不幸其父母俱亡于盛年。其弟妹六七人。俱未婚娶。彝锡时仅弱冠也。率育恐鞠。尽其诚心。及其异姓相聚。或不无盖底之圆方。而犹不以此而失其友爱之欢。顾以其丧祸零丁之初观之。宜其荡覆亡灭久矣。而乃能保其门户。守其祭祀者。不但其行义有以自立。而亦荷先灵鉴临。有以默佑之也。今者卖其京宅。移居于西郊之外而力田自给。名其堂曰联棣。噫。不待考其实而名已好矣。差
金大热。匹马奔哭。自六月以至仲冬。居外不肉葬然后复常。常曰。早知如此。何曾一日离也。逮于野隐公。其同气六人也。同奉母夫人。其奉养之诚。祭祀之礼。既化服乡邻。而其长枕大衾。日夕湛翕。咫尺往还。必与相随。野隐公性严。诸房少有过差。督责不少恕。而诸房皆逊谢自咎。而终不失和色焉。及其永感。则迫于贫穷。不免分离。其去母夫人祥禫未久也。相持不忍舍。行者顾送者泣。见者莫不掩泪。其第二房进士公资质尤卓异。尝到其金氏妹。见其贫甚而馁。泫然而悲。故金氏妹与之相对。不忍言贫也。公常顾恤其子女。婚嫁必自主张。及其既没而久也。金氏妹常曰。如失我慈父也。大抵吾家仁厚之风。耳目所及者如此矣。进士公有孙曰彝锡。不幸其父母俱亡于盛年。其弟妹六七人。俱未婚娶。彝锡时仅弱冠也。率育恐鞠。尽其诚心。及其异姓相聚。或不无盖底之圆方。而犹不以此而失其友爱之欢。顾以其丧祸零丁之初观之。宜其荡覆亡灭久矣。而乃能保其门户。守其祭祀者。不但其行义有以自立。而亦荷先灵鉴临。有以默佑之也。今者卖其京宅。移居于西郊之外而力田自给。名其堂曰联棣。噫。不待考其实而名已好矣。差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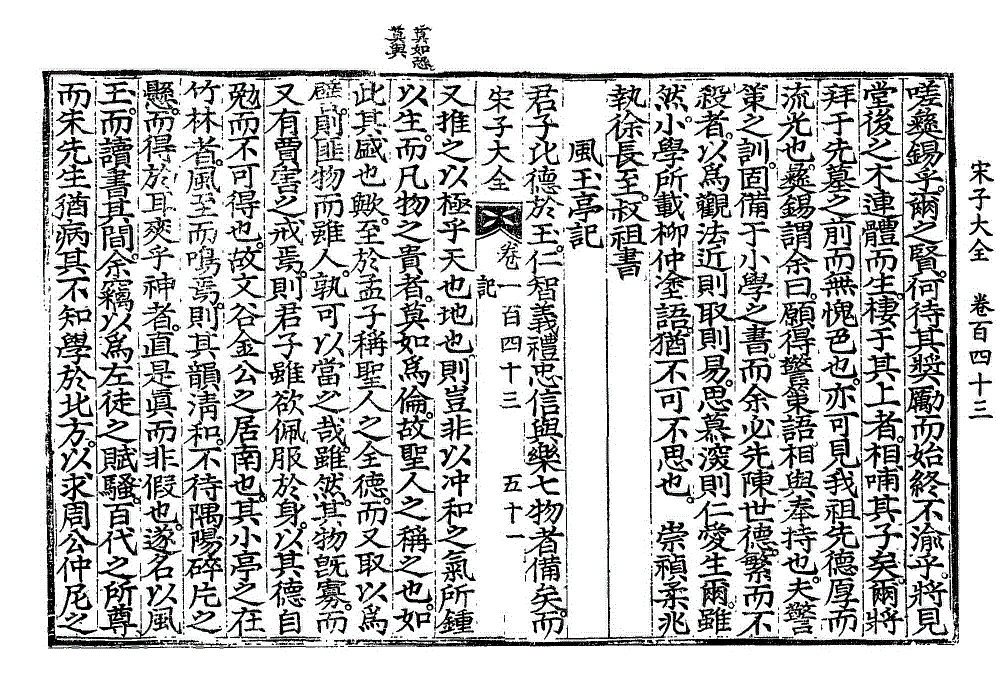 嗟彝锡乎。尔之贤。何待其奖励而始终不渝乎。将见堂后之木连体而生。栖于其上者。相哺其子矣。尔将拜于先墓之前而无愧色也。亦可见我祖先德厚而流光也。彝锡谓余曰。愿得警策语。相与奉持也。夫警策之训。固备于小学之书。而余必先陈世德。繁而不杀者。以为观法近则取则易。思慕深则仁爱生尔。虽然。小学所载柳仲涂语。犹不可不思也。 崇祯柔兆执徐长至。叔祖书。
嗟彝锡乎。尔之贤。何待其奖励而始终不渝乎。将见堂后之木连体而生。栖于其上者。相哺其子矣。尔将拜于先墓之前而无愧色也。亦可见我祖先德厚而流光也。彝锡谓余曰。愿得警策语。相与奉持也。夫警策之训。固备于小学之书。而余必先陈世德。繁而不杀者。以为观法近则取则易。思慕深则仁爱生尔。虽然。小学所载柳仲涂语。犹不可不思也。 崇祯柔兆执徐长至。叔祖书。风玉亭记
君子比德于玉。仁智义礼忠信与乐七物者备矣。而又推之以极乎天也地也。则岂非以冲和之气所钟以生。而凡物之贵者。莫如(莫如恐莫与)为伦。故圣人之称之也。如此其盛也欤。至于孟子称圣人之全德。而又取以为譬。则匪物而虽人。孰可以当之哉。虽然。其物既寡。而又有贾害之戒焉。则君子虽欲佩服于身。以其德自勉而不可得也。故文谷金公之居南也。其小亭之在竹林者。风至而鸣焉。则其韵清和。不待隅阳碎片之悬。而得于耳爽乎神者。直是真而非假也。遂名以风玉。而读书其间。余窃以为左徒之赋骚。百代之所尊。而朱先生犹病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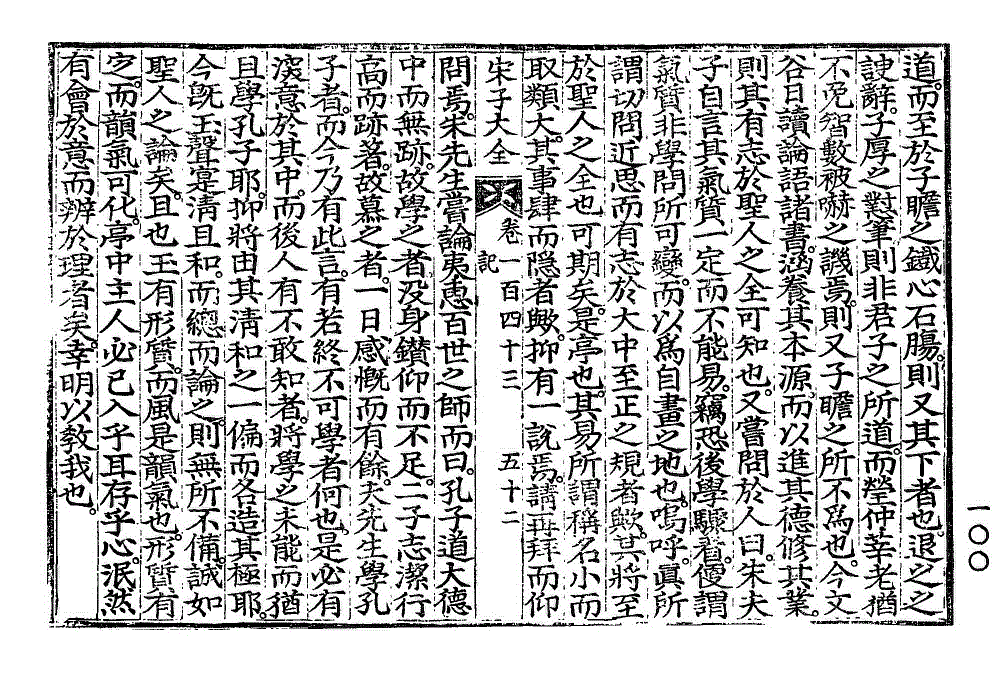 道。而至于子瞻之铁心石肠。则又其下者也。退之之谀辞。子厚之怼笔则非君子之所道。而莹仲,莘老犹不免智数被吓之讥焉。则又子瞻之所不为也。今文谷日读论语诸书。涵养其本源。而以进其德修其业。则其有志于圣人之全可知也。又尝问于人曰。朱夫子自言其气质一定而不能易。窃恐后学骤看。便谓气质非学问所可变。而以为自画之地也。呜呼。真所谓切问近思而有志于大中至正之规者欤。其将至于圣人之全也可期矣。是亭也。其易所谓称名小而取类大。其事肆而隐者欤。抑有一说焉。请再拜而仰问焉。朱先生尝论夷,惠百世之师而曰。孔子道大德中而无迹。故学之者。没身钻仰而不足。二子志洁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馀。夫先生学孔子者。而今乃有此言。有若终不可学者何也。是必有深意于其中。而后人有不敢知者。将学之未能而犹且学孔子耶。抑将由其清和之一偏而各造其极耶。今既玉声寔清且和。而总而论之。则无所不备。诚如圣人之论矣。且也玉有形质。而风是韵气也。形质有定。而韵气可化。亭中主人必已入乎耳存乎心。泯然有会于意而辨于理者矣。幸明以教我也。
道。而至于子瞻之铁心石肠。则又其下者也。退之之谀辞。子厚之怼笔则非君子之所道。而莹仲,莘老犹不免智数被吓之讥焉。则又子瞻之所不为也。今文谷日读论语诸书。涵养其本源。而以进其德修其业。则其有志于圣人之全可知也。又尝问于人曰。朱夫子自言其气质一定而不能易。窃恐后学骤看。便谓气质非学问所可变。而以为自画之地也。呜呼。真所谓切问近思而有志于大中至正之规者欤。其将至于圣人之全也可期矣。是亭也。其易所谓称名小而取类大。其事肆而隐者欤。抑有一说焉。请再拜而仰问焉。朱先生尝论夷,惠百世之师而曰。孔子道大德中而无迹。故学之者。没身钻仰而不足。二子志洁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馀。夫先生学孔子者。而今乃有此言。有若终不可学者何也。是必有深意于其中。而后人有不敢知者。将学之未能而犹且学孔子耶。抑将由其清和之一偏而各造其极耶。今既玉声寔清且和。而总而论之。则无所不备。诚如圣人之论矣。且也玉有形质。而风是韵气也。形质有定。而韵气可化。亭中主人必已入乎耳存乎心。泯然有会于意而辨于理者矣。幸明以教我也。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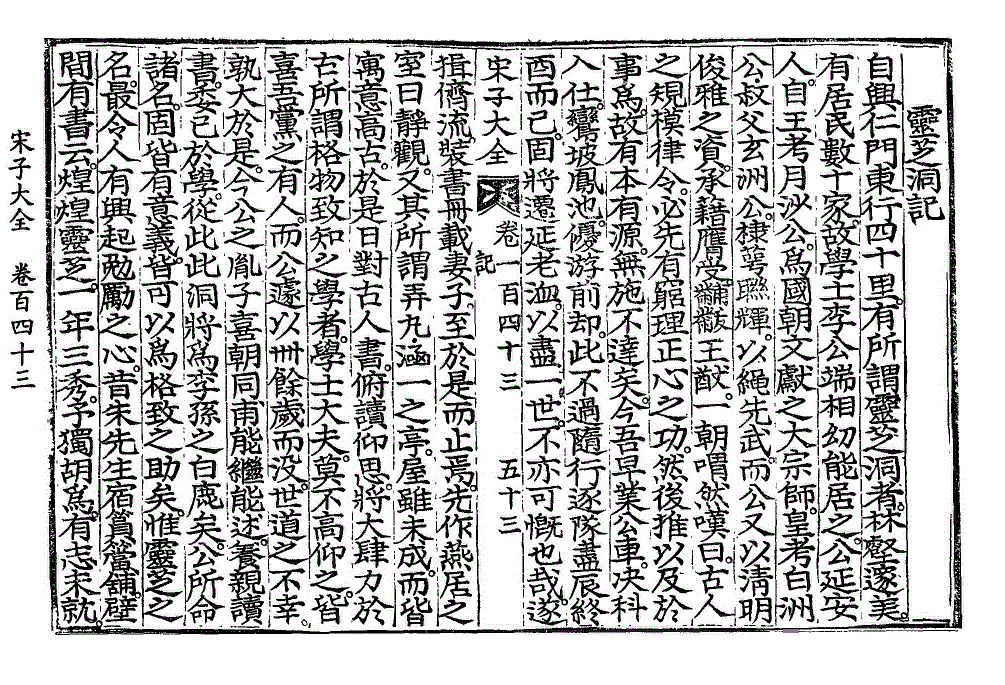 灵芝洞记
灵芝洞记自兴仁门东行四十里。有所谓灵芝洞者。林壑邃美。有居民数十家。故学士李公端相幼能居之。公延安人。自王考月沙公。为国朝文献之大宗师。皇考白洲公,叔父玄洲公。棣萼联辉。以绳先武。而公又以清明俊雅之资。承藉膺受。黼黻王猷。一朝喟然叹曰。古人之规模律令。必先有穷理正心之功。然后推以及于事为。故有本有源。无施不达矣。今吾早业公车。决科入仕。鸾坡凤池。优游前却。此不过随行逐队尽辰终酉而已。固将迁延老洫。以尽一世。不亦可慨也哉。遂揖侪流。装书册载妻子。至于是而止焉。先作燕居之室曰静观。又其所谓弄丸,涵一之亭。屋虽未成。而皆寓意高古。于是日对古人书。俯读仰思。将大肆力于古所谓格物致知之学者。学士大夫。莫不高仰之。皆喜吾党之有人。而公遽以卌馀岁而没。世道之不幸。孰大于是。今公之胤子喜朝同甫能继能述。养亲读书。委己于学。从此此洞将为李孙之白鹿矣。公所命诸名。固皆有意义。皆可以为格致之助矣。惟灵芝之名。最令人有兴起勉励之心。昔朱先生宿筼筜铺。壁间有书云。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胡为。有志未就。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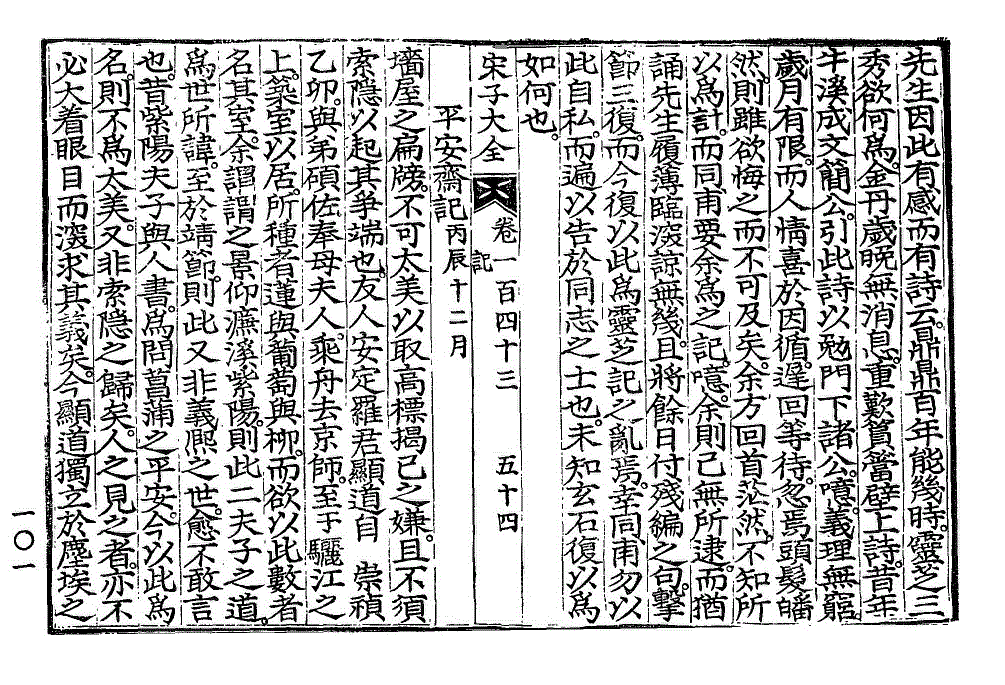 先生因此有感而有诗云。鼎鼎百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昔年牛溪成文简公。引此诗以勉门下诸公。噫。义理无穷。岁月有限。而人情喜于因循。迟回等待。忽焉头发皤然。则虽欲悔之而不可及矣。余方回首茫然。不知所以为计。而同甫要余为之记。噫。余则已无所逮。而犹诵先生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馀日付残编之句。击节三复。而今复以此为灵芝记之乱焉。幸同甫勿以此自私。而遍以告于同志之士也。未知玄石复以为如何也。
先生因此有感而有诗云。鼎鼎百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昔年牛溪成文简公。引此诗以勉门下诸公。噫。义理无穷。岁月有限。而人情喜于因循。迟回等待。忽焉头发皤然。则虽欲悔之而不可及矣。余方回首茫然。不知所以为计。而同甫要余为之记。噫。余则已无所逮。而犹诵先生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馀日付残编之句。击节三复。而今复以此为灵芝记之乱焉。幸同甫勿以此自私。而遍以告于同志之士也。未知玄石复以为如何也。平安斋记(丙辰十二月)
墙屋之扁榜。不可太美以取高标揭己之嫌。且不须索隐以起其争端也。友人安定罗君显道自 崇祯乙卯。与弟硕佐奉母夫人。乘舟去京师。至于骊江之上。筑室以居。所种者莲与葡萄与柳。而欲以此数者名其室。余谓谓之景仰濂溪,紫阳。则此二夫子之道。为世所讳。至于靖节。则此又非义熙之世。愈不敢言也。昔紫阳夫子与人书。为问菖蒲之平安。今以此为名。则不为太美。又非索隐之归矣。人之见之者。亦不必大着眼目而深求其义矣。今显道独立于尘埃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三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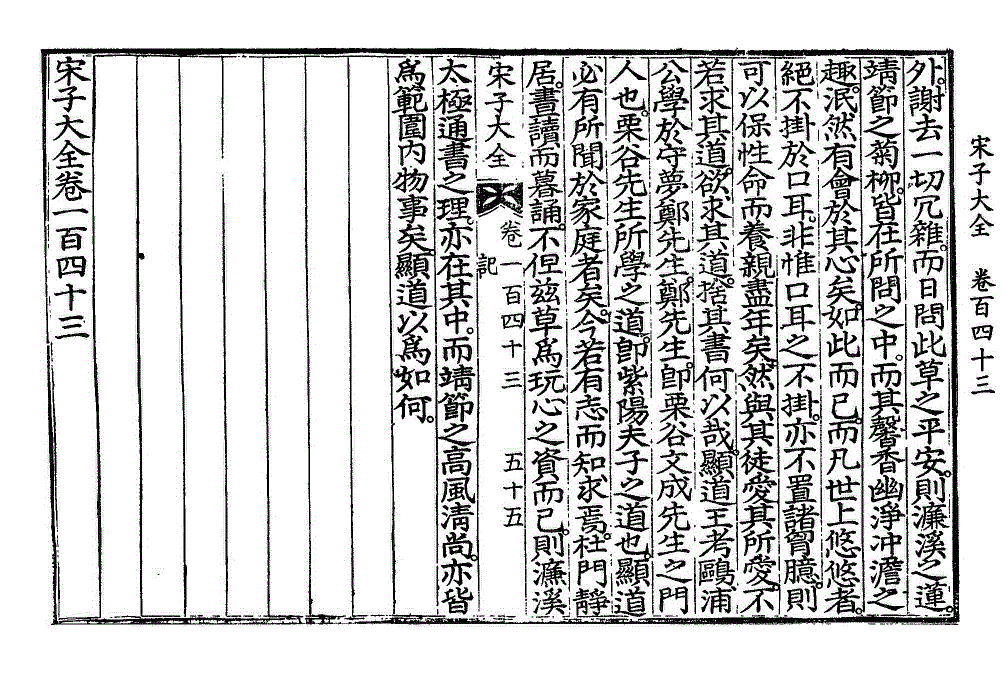 外。谢去一切冗杂。而日问此草之平安。则濂溪之莲。靖节之菊柳。皆在所问之中。而其馨香幽净冲澹之趣。泯然有会于其心矣。如此而已。而凡世上悠悠者。绝不挂于口耳。非惟口耳之不挂。亦不置诸胸臆。则可以保性命而养亲尽年矣。然与其徒爱其所爱。不若求其道。欲求其道。舍其书何以哉。显道王考鸥浦公学于守梦郑先生。郑先生。即栗谷,文成先生之门人也。栗谷先生所学之道。即紫阳夫子之道也。显道必有所闻于家庭者矣。今若有志而知求焉。杜门静居。昼读而暮诵。不但兹草为玩心之资而已。则濂溪太极通书之理。亦在其中。而靖节之高风清尚。亦皆为范围内物事矣。显道以为如何。
外。谢去一切冗杂。而日问此草之平安。则濂溪之莲。靖节之菊柳。皆在所问之中。而其馨香幽净冲澹之趣。泯然有会于其心矣。如此而已。而凡世上悠悠者。绝不挂于口耳。非惟口耳之不挂。亦不置诸胸臆。则可以保性命而养亲尽年矣。然与其徒爱其所爱。不若求其道。欲求其道。舍其书何以哉。显道王考鸥浦公学于守梦郑先生。郑先生。即栗谷,文成先生之门人也。栗谷先生所学之道。即紫阳夫子之道也。显道必有所闻于家庭者矣。今若有志而知求焉。杜门静居。昼读而暮诵。不但兹草为玩心之资而已。则濂溪太极通书之理。亦在其中。而靖节之高风清尚。亦皆为范围内物事矣。显道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