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x 页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记
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0H 页
 憃愚堂记
憃愚堂记宗人殿中君宋国荩。某年月日。构所居之室于白达村。其伯仲氏之家在其南。叔氏之家在其北。诸从子侄群族环列左右。君尝仕于朝。以憃愚之目被参而归曰。名我足矣。遂以扁其正堂之楣曰。吾将守此以老而死也。日与其兄弟族党。朝夕游从。诩诩然不知老之将至也。真所谓虐之而乐之者也。余惟愚者智之反。诚非美名。然自圣人称以渊,羔之后。后之人多自称而不厌也。至于憃则騃昏之名。非人之所愿也。然人以是归之。而君受而不辞。又将以自詑焉。此古滑稽之流之所为欤。然记数民之蔽者。憃其一也。而释之者以为情不浇诡也。若是则是亦未尝为不美。而宜在所让也。又周礼三赦之科。憃实与焉。故朝廷曾又叙复其官。此实恕憃之道也。然则是名也。于君。为得乎为失乎。兹有一事。好与族党抵掌而谈噱者。君与同春公比邻甚相爱。而与草庐公少相善。昨者草庐抵书于同春。谓君物故而相吊焉。昔东坡亦尝遭此而曰。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憃愚之称。亦将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0L 页
 以此而推之可也。惟是世故变嬗。伯仲氏先后谢世。而叔氏亦从宦远去。君孤孑踽凉。令人恻怆矣。君今又弃家迁徙。而其堂岿然空荒。甚可惜也。君尝要余题其扁。余意其戏而亦戏而副之。君终不弃而揭之。岂以余笔正合于此堂也耶。知所择而得其人焉。君真不憃愚也。 崇祯庚戌孟春日。宗人宋时烈记。
以此而推之可也。惟是世故变嬗。伯仲氏先后谢世。而叔氏亦从宦远去。君孤孑踽凉。令人恻怆矣。君今又弃家迁徙。而其堂岿然空荒。甚可惜也。君尝要余题其扁。余意其戏而亦戏而副之。君终不弃而揭之。岂以余笔正合于此堂也耶。知所择而得其人焉。君真不憃愚也。 崇祯庚戌孟春日。宗人宋时烈记。高敞县平近堂记
牟阳。湖南之最小邑也。宋侯一卿始至。即誇其苍松老槐。又因辛白麓应时诗。知有万竹小池之趣。余与侯自少同里讲睦。熟知其抱负矣。意其以为不足为。而只痛扫溉。日哦其间。如崔博陵之为者。顾乃削衣贬食。以其赢馀。占地徵龟。以新衙舍。又治一堂于其傍。而取周公所戒鲁公语。扁以平近。夫以匹夫之势。处闾巷之间。其亲爱同胞之心。犹且随其分而有所施矣。今此邑虽小。为官者日见其饥寒癃疲之状。而不以为意。则一膜之外。便成胡越。而食焉怠事之责。乌得免乎。陵令之为吏隐。亦不如是矣。今将以此二字。常寓于目。使其无衣者来告其寒。无食者来告其饥。而痒疴疾痛者。举得以告其病。然后得以施其抚摩之仁矣。彼崔博陵者。初亦岂欲负丞。而丞乃负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1H 页
 故不得已而如斯矣。然平易近民。固为政之本。然德愈全则责愈备。故圣人必曰临民以庄。又曰不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则未善也。必须先之以平近。使各得输其情。而亦必持己庄敬。使民不慢。然后渐可以教民以礼。而为政之道始备矣。而况周公之训。实以鲁公之政不如太公而有是说。然朱子以为太公初封。做得不大段好。便有些杂伯气象。则岂但以平易近民。为尽善尽美也哉。虽然平易近民。亦非横目自营者之所可能。则为政者亦不可不察切己之实病。而蕲望于向上之事。此又不可不知也。侯自其先大夫。出入于溪门函丈。而得有所闻。则侯必有得于晨昏之际者。故终始言之。侯名国士。以友爱称于宗党。故亦将推其心于吏民云。时 崇祯庚戌馀分之下浣。宗人宋时烈记。
故不得已而如斯矣。然平易近民。固为政之本。然德愈全则责愈备。故圣人必曰临民以庄。又曰不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则未善也。必须先之以平近。使各得输其情。而亦必持己庄敬。使民不慢。然后渐可以教民以礼。而为政之道始备矣。而况周公之训。实以鲁公之政不如太公而有是说。然朱子以为太公初封。做得不大段好。便有些杂伯气象。则岂但以平易近民。为尽善尽美也哉。虽然平易近民。亦非横目自营者之所可能。则为政者亦不可不察切己之实病。而蕲望于向上之事。此又不可不知也。侯自其先大夫。出入于溪门函丈。而得有所闻。则侯必有得于晨昏之际者。故终始言之。侯名国士。以友爱称于宗党。故亦将推其心于吏民云。时 崇祯庚戌馀分之下浣。宗人宋时烈记。益山郡埙篪(一作篪)堂记
今 上甲辰。仲氏视篆金马。见其官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又见其所不可无者皆无也。遂先治别堂于衙舍之前。将次第修建矣。已而意有所不乐。即解归。家弟隔一年代之。相去仅七月矣。即欲为仲氏之所欲为者。而连岁不登。惟赈饥是事。兼且营将设镇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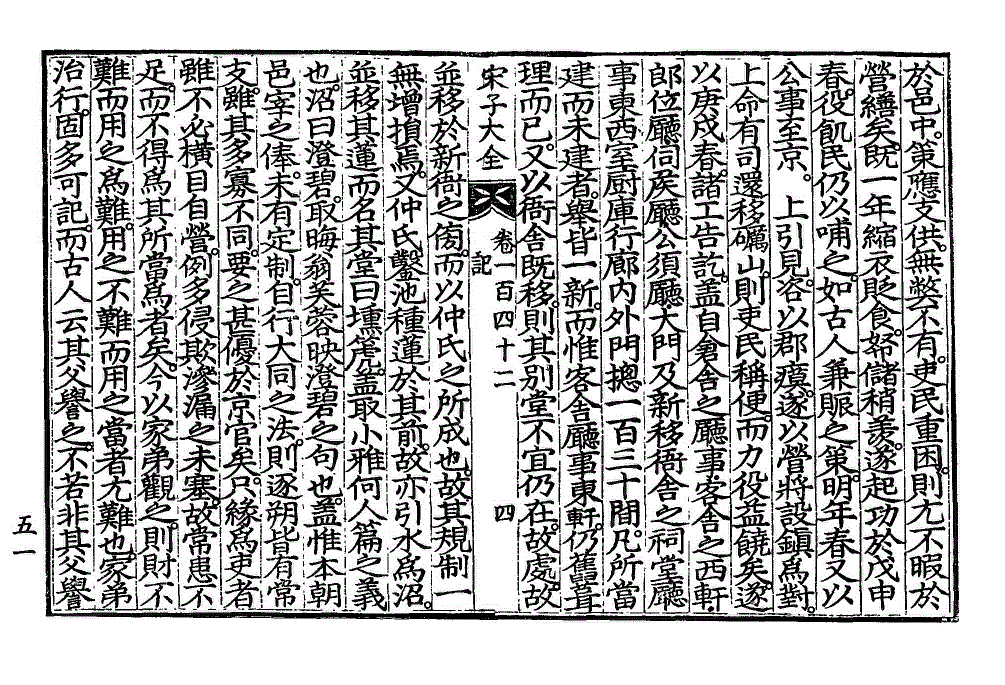 于邑中。策应支供。无弊不有。吏民重困。则尤不暇于营缮矣。既一年缩衣贬食。帑储稍羡。遂起功于戊申春。役饥民仍以哺之。如古人兼赈之策。明年春又以公事至京。 上引见。咨以郡瘼。遂以营将设镇为对。上命有司还移砺山。则吏民称便。而力役益饶矣。遂以庚戌春。诸工告讫。盖自仓舍之厅事,客舍之西轩,郎位厅,伺侯(一作候)厅,公须厅,大门及新移衙舍之祠堂,厅事东西室,厨库行廊内外门总一百三十间。凡所当建而未建者。举皆一新。而惟客舍厅事东轩。仍旧葺理而已。又以衙舍既移。则其别堂不宜仍在故处。故并移于新衙之傍。而以仲氏之所成也。故其规制一无增损焉。又仲氏凿池种莲于其前。故亦引水为沼。并移其莲而名其堂曰埙篪(一作篪)。盖取小雅何人篇之义也。沼曰澄碧。取晦翁芙蓉映澄碧之句也。盖惟本朝邑宰之俸。未有定制。自行大同之法。则逐朔皆有常支。虽其多寡不同。要之甚优于京官矣。只缘为吏者虽不必横目自营。例多侵欺渗漏之未塞。故常患不足。而不得为其所当为者矣。今以家弟观之。则财不难而用之为难。用之不难而用之当者尤难也。家弟治行。固多可记。而古人云其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誉
于邑中。策应支供。无弊不有。吏民重困。则尤不暇于营缮矣。既一年缩衣贬食。帑储稍羡。遂起功于戊申春。役饥民仍以哺之。如古人兼赈之策。明年春又以公事至京。 上引见。咨以郡瘼。遂以营将设镇为对。上命有司还移砺山。则吏民称便。而力役益饶矣。遂以庚戌春。诸工告讫。盖自仓舍之厅事,客舍之西轩,郎位厅,伺侯(一作候)厅,公须厅,大门及新移衙舍之祠堂,厅事东西室,厨库行廊内外门总一百三十间。凡所当建而未建者。举皆一新。而惟客舍厅事东轩。仍旧葺理而已。又以衙舍既移。则其别堂不宜仍在故处。故并移于新衙之傍。而以仲氏之所成也。故其规制一无增损焉。又仲氏凿池种莲于其前。故亦引水为沼。并移其莲而名其堂曰埙篪(一作篪)。盖取小雅何人篇之义也。沼曰澄碧。取晦翁芙蓉映澄碧之句也。盖惟本朝邑宰之俸。未有定制。自行大同之法。则逐朔皆有常支。虽其多寡不同。要之甚优于京官矣。只缘为吏者虽不必横目自营。例多侵欺渗漏之未塞。故常患不足。而不得为其所当为者矣。今以家弟观之。则财不难而用之为难。用之不难而用之当者尤难也。家弟治行。固多可记。而古人云其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誉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2H 页
 之。兄弟与父子。所争几何哉。故只书其屋宇之作止年月及所作之间架焉。若其名堂之义则以一家之私而揭之公馆。似若有招议者。然兄弟之伦。是通天地之公理。天下岂有伦外之人欤。后之继而来者。无以为一人之私。而因此一端。推广而教于民。则不待闭閤。不必下泪。而自无高陵清河之民矣。其于为政之本。殆庶几焉尔。家弟名时焘字诚甫。其先恩津人也。
之。兄弟与父子。所争几何哉。故只书其屋宇之作止年月及所作之间架焉。若其名堂之义则以一家之私而揭之公馆。似若有招议者。然兄弟之伦。是通天地之公理。天下岂有伦外之人欤。后之继而来者。无以为一人之私。而因此一端。推广而教于民。则不待闭閤。不必下泪。而自无高陵清河之民矣。其于为政之本。殆庶几焉尔。家弟名时焘字诚甫。其先恩津人也。冽泉亭记
丫溪子尝将金帛。往使燕。自栅门至其都城。历观 皇朝时控御城池。文物制作。其遗迹尚皆可考。不胜殷墟箕子之泣。既归屡以密告于 上者。皆天下事也。遂于其居之后。作冽泉之亭。盖取曹风下泉之义也。其诗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噫。虽生在丙丁之后者。犹不无阴阳夏夷之辨。况吾沐浴 皇朝之风化。游泳 帝德之浸润者乎。又况壬丁倭变。靡 皇上至诚东顾。则其无国久矣。况复有此身乎。及至今日。追思反顾。至于血泣而不已者。盖天理民彝之不期然而然者矣。试于云收日朗之时。登斯亭也。北望中朝而想像三百年升平遗韵。而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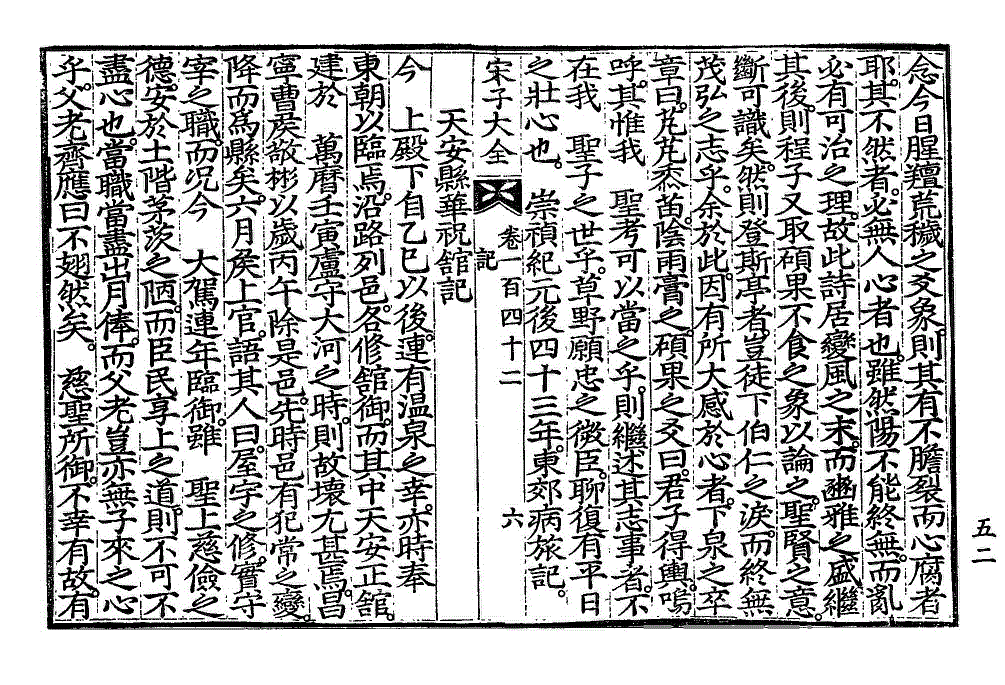 念今日腥膻荒秽之爻象。则其有不胆裂而心腐者耶。其不然者。必无人心者也。虽然阳不能终无。而乱必有可治之理。故此诗居变风之末。而豳雅之盛继其后。则程子又取硕果不食之象以论之。圣贤之意。断可识矣。然则登斯亭者。岂徒下伯仁之泪。而终无茂弘之志乎。余于此。因有所大感于心者。下泉之卒章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硕果之爻曰。君子得舆。呜呼。其惟我 圣考可以当之乎。则继述其志事者。不在我 圣子之世乎。草野愿忠之微臣。聊复有平日之壮心也。 崇祯纪元后四十三年。东郊病旅记。
念今日腥膻荒秽之爻象。则其有不胆裂而心腐者耶。其不然者。必无人心者也。虽然阳不能终无。而乱必有可治之理。故此诗居变风之末。而豳雅之盛继其后。则程子又取硕果不食之象以论之。圣贤之意。断可识矣。然则登斯亭者。岂徒下伯仁之泪。而终无茂弘之志乎。余于此。因有所大感于心者。下泉之卒章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硕果之爻曰。君子得舆。呜呼。其惟我 圣考可以当之乎。则继述其志事者。不在我 圣子之世乎。草野愿忠之微臣。聊复有平日之壮心也。 崇祯纪元后四十三年。东郊病旅记。天安县华祝馆记
今 上殿下自乙巳以后。连有温泉之幸。亦时奉 东朝以临焉。沿路列邑。各修馆御。而其中天安正馆。建于 万历壬寅卢守大河之时。则故坏尤甚焉。昌宁曹侯敬彬以岁丙午除是邑。先时邑有犯常之变。降而为县矣。六月侯上官。语其人曰。屋宇之修。实守宰之职。而况今 大驾连年临御。虽 圣上慈俭之德。安于土阶茅茨之陋。而臣民享上之道。则不可不尽心也。当职当尽出月俸。而父老岂亦无子来之心乎。父老齐应曰不翅然矣。 慈圣所御。不幸有故。有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3H 页
 不可仍旧者。而其事体又有不敢专辄者。故监司任公义伯令侯往白于大臣。而归以驿闻。则大臣许以改为。而令有司为给米布。亦有闻而相助者矣。遂先治正馆之东轩。次改 慈圣御室。而廊厅中大厅武库诸宇。无不重新矣。戊申监司闵公维重谓侯曰。今兹苟完矣。若并治西轩。岂不尽美矣乎。侯亦以一篑之亏为惜。而如其命焉。今年庚戌春。工告讫事。总大小凡三十九间。而前后见助者。庆尚监司李公泰渊。统制使李枝馨,金镜。本道兵使李元老。全罗兵使闵震益也。既而侯问其所以名者。且以记文为请。余曰诸人之越封而相助者。岂所以私于侯者。然则诸公以财。而余以文字之末。寓其区区蝼蚁之诚。亦其义然也。昔帝尧观于华。华封人祝之以寿富多男子。今日臣民为 圣上愿之者。岂外于此哉。如取此义名其馆曰华祝则其庶矣乎。或曰寿与多男子。固所愿之大者。而 圣上方以外本内末为戒。富亦可愿者欤。曰富岂府库之藏之谓欤。时和岁丰。家给人足。而礼乐可兴者。斯岂非吾 圣上之富欤。不幸数年以来。饥馑荐臻。人民多死。 圣上忧劳于上。恻怛之教屡下。闻之者无不感泣矣。倘天心悔祸。雨旸时若。多
不可仍旧者。而其事体又有不敢专辄者。故监司任公义伯令侯往白于大臣。而归以驿闻。则大臣许以改为。而令有司为给米布。亦有闻而相助者矣。遂先治正馆之东轩。次改 慈圣御室。而廊厅中大厅武库诸宇。无不重新矣。戊申监司闵公维重谓侯曰。今兹苟完矣。若并治西轩。岂不尽美矣乎。侯亦以一篑之亏为惜。而如其命焉。今年庚戌春。工告讫事。总大小凡三十九间。而前后见助者。庆尚监司李公泰渊。统制使李枝馨,金镜。本道兵使李元老。全罗兵使闵震益也。既而侯问其所以名者。且以记文为请。余曰诸人之越封而相助者。岂所以私于侯者。然则诸公以财。而余以文字之末。寓其区区蝼蚁之诚。亦其义然也。昔帝尧观于华。华封人祝之以寿富多男子。今日臣民为 圣上愿之者。岂外于此哉。如取此义名其馆曰华祝则其庶矣乎。或曰寿与多男子。固所愿之大者。而 圣上方以外本内末为戒。富亦可愿者欤。曰富岂府库之藏之谓欤。时和岁丰。家给人足。而礼乐可兴者。斯岂非吾 圣上之富欤。不幸数年以来。饥馑荐臻。人民多死。 圣上忧劳于上。恻怛之教屡下。闻之者无不感泣矣。倘天心悔祸。雨旸时若。多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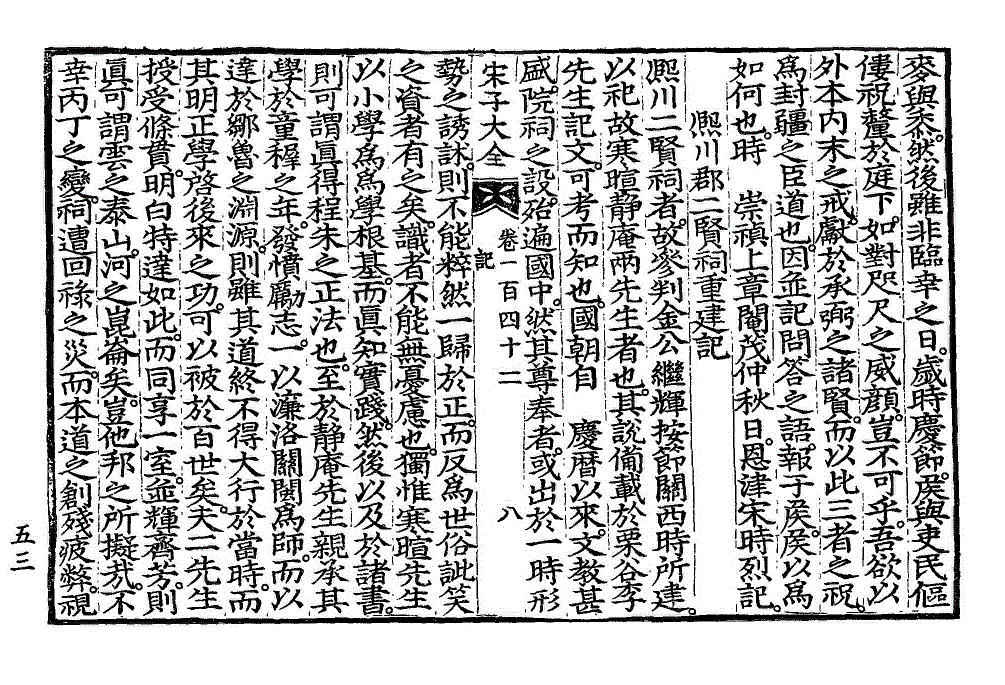 麦与黍。然后虽非临幸之日。岁时庆节。侯与吏民伛偻祝釐于庭下。如对咫尺之威颜。岂不可乎。吾欲以外本内末之戒。献于承弼之诸贤。而以此三者之祝。为封疆之臣道也。因并记问答之语。报于侯。侯以为如何也。时 崇祯上章阉茂仲秋日。恩津宋时烈记。
麦与黍。然后虽非临幸之日。岁时庆节。侯与吏民伛偻祝釐于庭下。如对咫尺之威颜。岂不可乎。吾欲以外本内末之戒。献于承弼之诸贤。而以此三者之祝。为封疆之臣道也。因并记问答之语。报于侯。侯以为如何也。时 崇祯上章阉茂仲秋日。恩津宋时烈记。熙川郡二贤祠重建记
熙川二贤祠者。故参判金公继辉按节关西时所建。以祀故寒暄,静庵两先生者也。其说备载于栗谷李先生记文。可考而知也。国朝自 庆历以来。文教甚盛。院祠之设。殆遍国中。然其尊奉者。或出于一时形势之诱訹。则不能粹然一归于正。而反为世俗訾笑之资者有之矣。识者不能无忧虑也。独惟寒暄先生以小学为为学根基。而真知实践。然后以及于诸书。则可谓真得程朱之正法也。至于静庵先生亲承其学于童稚之年。发愤励志。一以濂洛关闽为师。而以达于邹鲁之渊源。则虽其道终不得大行于当时。而其明正学启后来之功。可以被于百世矣。夫二先生授受条贯。明白特达如此。而同享一室。并辉齐芳。则真可谓云之泰山。河之昆崙矣。岂他邦之所拟哉。不幸丙丁之变。祠遭回禄之灾。而本道之创残疲弊。视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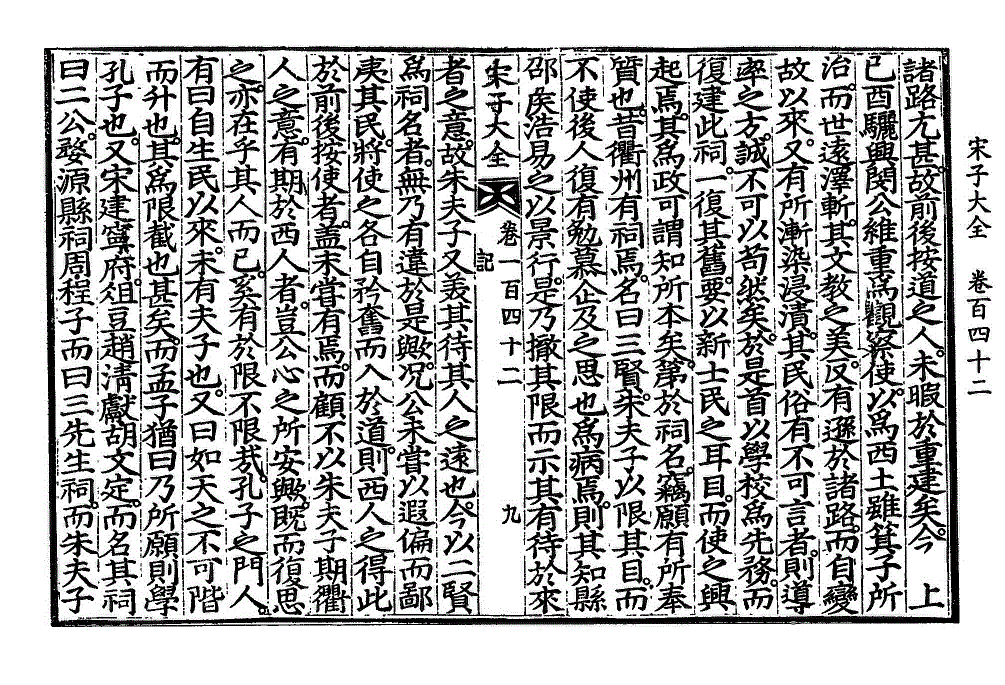 诸路尤甚。故前后按道之人。未暇于重建矣。今 上己酉骊兴闵公维重为观察使。以为西土虽箕子所治。而世远泽斩。其文教之美。反有逊于诸路。而自变故以来。又有所渐染浸渍。其民俗有不可言者。则导率之方。诚不可以苟然矣。于是首以学校为先务。而复建此祠。一复其旧。要以新士民之耳目。而使之兴起焉。其为政可谓知所本矣。第于祠名。窃愿有所奉质也。昔衢州有祠焉。名曰三贤。朱夫子以限其目。而不使后人复有勉慕企及之思也为病焉。则其知县邵侯浩易之以景行。是乃撤其限而示其有待于来者之意。故朱夫子又美其待其人之远也。今以二贤为祠名者。无乃有违于是欤。况公未尝以遐偏而鄙夷其民。将使之各自矜奋而入于道。则西人之得此于前后按使者。盖未尝有焉。而顾不以朱夫子期衢人之意。有期于西人者。岂公心之所安欤。既而复思之。亦在乎其人而已。奚有于限不限哉。孔子之门人。有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又曰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为限截也甚矣。而孟子犹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又宋建宁府。俎豆赵清献,胡文定。而名其祠曰二公。婺源县祠周,程子而曰三先生祠。而朱夫子
诸路尤甚。故前后按道之人。未暇于重建矣。今 上己酉骊兴闵公维重为观察使。以为西土虽箕子所治。而世远泽斩。其文教之美。反有逊于诸路。而自变故以来。又有所渐染浸渍。其民俗有不可言者。则导率之方。诚不可以苟然矣。于是首以学校为先务。而复建此祠。一复其旧。要以新士民之耳目。而使之兴起焉。其为政可谓知所本矣。第于祠名。窃愿有所奉质也。昔衢州有祠焉。名曰三贤。朱夫子以限其目。而不使后人复有勉慕企及之思也为病焉。则其知县邵侯浩易之以景行。是乃撤其限而示其有待于来者之意。故朱夫子又美其待其人之远也。今以二贤为祠名者。无乃有违于是欤。况公未尝以遐偏而鄙夷其民。将使之各自矜奋而入于道。则西人之得此于前后按使者。盖未尝有焉。而顾不以朱夫子期衢人之意。有期于西人者。岂公心之所安欤。既而复思之。亦在乎其人而已。奚有于限不限哉。孔子之门人。有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又曰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为限截也甚矣。而孟子犹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又宋建宁府。俎豆赵清献,胡文定。而名其祠曰二公。婺源县祠周,程子而曰三先生祠。而朱夫子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4L 页
 勉建之为士者则曰。诸君望其容貌而起肃敬之心。考其言行而激贪懦之志。然后精思熟讲。反之于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果能达于圣贤之事。则是区区平日所望于诸君也。又谕婺之学者则使观周子书而曰。其大指不过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是乃所谓伊尹之志颜子之学。而程氏传之。以觉斯人者。亦岂有以外乎。诸君日用之间哉。由是而用力焉。则庶几乎三先生之志不坠于地矣。然则朱夫子曷尝以祠名之有所限。而不以其所祠之人之道德学问而期之于其人也。今西土之人。以夫子所以谕于建婺之士者。自勉而不已焉。则其所以撤其限于衢州。而待其人之深意。亦可以不负矣。此岂非闵公今日之心也欤。呜呼。西土之人。勿以地之荒僻时之危乱。而甘于暴弃之归也。庚戌仲秋。后学恩津宋时烈记。
勉建之为士者则曰。诸君望其容貌而起肃敬之心。考其言行而激贪懦之志。然后精思熟讲。反之于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果能达于圣贤之事。则是区区平日所望于诸君也。又谕婺之学者则使观周子书而曰。其大指不过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是乃所谓伊尹之志颜子之学。而程氏传之。以觉斯人者。亦岂有以外乎。诸君日用之间哉。由是而用力焉。则庶几乎三先生之志不坠于地矣。然则朱夫子曷尝以祠名之有所限。而不以其所祠之人之道德学问而期之于其人也。今西土之人。以夫子所以谕于建婺之士者。自勉而不已焉。则其所以撤其限于衢州。而待其人之深意。亦可以不负矣。此岂非闵公今日之心也欤。呜呼。西土之人。勿以地之荒僻时之危乱。而甘于暴弃之归也。庚戌仲秋。后学恩津宋时烈记。清风馆重修记
清风为郡。最居湖西之上游。地瘠民稀。号为一道之岩邑。然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又俗朴事简。官吏只课梅花月色。其清致可知也。以故士大夫厌城市尚清疏者。不嫌于公诵而求之。既求而得之。则又自詑于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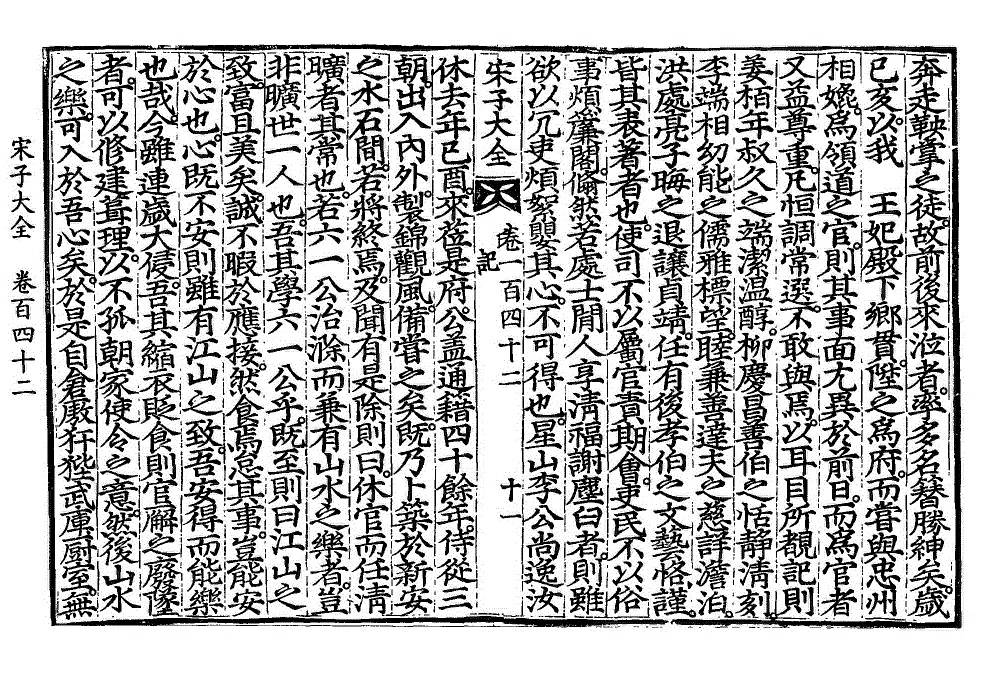 奔走鞅掌之徒。故前后来涖者。率多名簪胜绅矣。岁己亥。以我 王妃殿下乡贯。升之为府。而尝与忠州相媲。为领道之官。则其事面尤异于前日。而为官者又益尊重。凡恒调常选。不敢与焉。以耳目所睹记则姜柏年叔久之端洁温醇。柳庆昌善伯之恬静清刻。李端相幼能之儒雅标望。睦兼善达夫之慈详澹泊。洪处亮子晦之退让贞靖。任有后孝伯之文艺恪谨。皆其表著者也。使司不以属官责期会。吏民不以俗事烦帘阁。翛然若处士閒人享清福谢尘臼者。则虽欲以冗吏烦絮婴其心。不可得也。星山李公尚逸汝休去年己酉。来莅是府。公盖通籍四十馀年。侍从三朝。出入内外。制锦观风。备尝之矣。既乃卜筑于新安之水石间。若将终焉。及闻有是除则曰。休官而任清旷者其常也。若六一公治滁而兼有山水之乐者。岂非旷世一人也。吾其学六一公乎。既至则曰江山之致。富且美矣。诚不暇于应接。然食焉怠其事。岂能安于心也。心既不安则虽有江山之致。吾安得而能乐也哉。今虽连岁大侵。吾其缩衣贬食则官廨之废坠者。可以修建葺理。以不孤朝家使令之意。然后山水之乐。可入于吾心矣。于是自仓廒犴狴武库厨室。无
奔走鞅掌之徒。故前后来涖者。率多名簪胜绅矣。岁己亥。以我 王妃殿下乡贯。升之为府。而尝与忠州相媲。为领道之官。则其事面尤异于前日。而为官者又益尊重。凡恒调常选。不敢与焉。以耳目所睹记则姜柏年叔久之端洁温醇。柳庆昌善伯之恬静清刻。李端相幼能之儒雅标望。睦兼善达夫之慈详澹泊。洪处亮子晦之退让贞靖。任有后孝伯之文艺恪谨。皆其表著者也。使司不以属官责期会。吏民不以俗事烦帘阁。翛然若处士閒人享清福谢尘臼者。则虽欲以冗吏烦絮婴其心。不可得也。星山李公尚逸汝休去年己酉。来莅是府。公盖通籍四十馀年。侍从三朝。出入内外。制锦观风。备尝之矣。既乃卜筑于新安之水石间。若将终焉。及闻有是除则曰。休官而任清旷者其常也。若六一公治滁而兼有山水之乐者。岂非旷世一人也。吾其学六一公乎。既至则曰江山之致。富且美矣。诚不暇于应接。然食焉怠其事。岂能安于心也。心既不安则虽有江山之致。吾安得而能乐也哉。今虽连岁大侵。吾其缩衣贬食则官廨之废坠者。可以修建葺理。以不孤朝家使令之意。然后山水之乐。可入于吾心矣。于是自仓廒犴狴武库厨室。无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5L 页
 一不新。而其中斯馆。乃其正处。故最为良构。而制又魁杰。丹雘之施。亦不甚陋。然民则不知也。东有寒碧楼凝清阁。西有观水堂梅月轩。而北临长江。南对罗山。其可谓两相宜矣。余尝以公命书清风馆三字。公不鄙而揭之楣间。则无乃近于佛头铺粪耶。是可愧也。盖昔六一公朝暮四时于山水之乐。若无意于官下一事。而犹作丰乐之亭。以侈其谣俗山川。盖以艺祖遗迹之所在也。况此府者。实我朝蜀涂之乡。而遂有 圣子之庆。则此岂止于艺祖之暂然遗迹之比哉。然则凡其地之羽毛根荄。皆当张皇贲饰之不暇。况使其官府任其颓圮荒残。而同于一废邑而已。则岂不有歉于六一公乎。李公之始来也。盖慕六一公之趣。故今记其兴作之由。亦藉六一公为说焉。览者或有以谅其意也。时 崇祯上章阉茂仲秋日。恩津宋时烈记。
一不新。而其中斯馆。乃其正处。故最为良构。而制又魁杰。丹雘之施。亦不甚陋。然民则不知也。东有寒碧楼凝清阁。西有观水堂梅月轩。而北临长江。南对罗山。其可谓两相宜矣。余尝以公命书清风馆三字。公不鄙而揭之楣间。则无乃近于佛头铺粪耶。是可愧也。盖昔六一公朝暮四时于山水之乐。若无意于官下一事。而犹作丰乐之亭。以侈其谣俗山川。盖以艺祖遗迹之所在也。况此府者。实我朝蜀涂之乡。而遂有 圣子之庆。则此岂止于艺祖之暂然遗迹之比哉。然则凡其地之羽毛根荄。皆当张皇贲饰之不暇。况使其官府任其颓圮荒残。而同于一废邑而已。则岂不有歉于六一公乎。李公之始来也。盖慕六一公之趣。故今记其兴作之由。亦藉六一公为说焉。览者或有以谅其意也。时 崇祯上章阉茂仲秋日。恩津宋时烈记。平壤府乙支公祠宇记
上之九年戊申。韩山李公泰渊为平安监司。走书于余曰。古高句丽乙支公文德。当杨广来侵之日。能以偏师抗御百万之众。以存其国家。以保其民人。自是号称强国。虽以金元之好暴。每有所慑惮而不敢肆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6H 页
 其虐。其功利之所及者大且远矣。以故国史记之。遗庶思之。今欲立祠以享之。以酬其庸如何。余发书愀然曰。有是哉。古今之异势也。当彼时以东偏三分之一。而其武略之竞尚如此。其后乃有六千里。为雠人役之叹。何也。岂系得人之如何也耶。然则虽越宇宙而其追慕而不忘也。宜如朝暮遇者矣。况其旧国之遗黎也耶。且夫西土之文献。其无徵久矣。而公能肇启词源。卓然为众作之首。则不但戎功之为可记也。未几李公奄以柩归。故祠垂成而中辍。西民追惜之不已矣。骊兴闵公维重继其职。即踵以成之。得七月乙亥奉位版。妥侑如礼。而以书来请记。窃惟圣王之制祀典也。非徒先圣贤而已。凡有勋庸者。皆得与焉。故周官有司勋氏铭书祭烝之礼。尚书亦有纪功元祀之文。而记曰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能捍大患则祀之。今乙支公可谓御大菑捍大患。而死勤事劳定国。则其记功作祀而载之于司勋者。在所不已也。岂可以事在前代。而遂不崇报也。李公之意可谓美矣。而闵公之成其美者。尤见其公天下之善。而无间于人己也。抑又论之。当时以蕞尔属国。抗衡中夏。屠戮王师。困迫乘舆。以大失侯度
其虐。其功利之所及者大且远矣。以故国史记之。遗庶思之。今欲立祠以享之。以酬其庸如何。余发书愀然曰。有是哉。古今之异势也。当彼时以东偏三分之一。而其武略之竞尚如此。其后乃有六千里。为雠人役之叹。何也。岂系得人之如何也耶。然则虽越宇宙而其追慕而不忘也。宜如朝暮遇者矣。况其旧国之遗黎也耶。且夫西土之文献。其无徵久矣。而公能肇启词源。卓然为众作之首。则不但戎功之为可记也。未几李公奄以柩归。故祠垂成而中辍。西民追惜之不已矣。骊兴闵公维重继其职。即踵以成之。得七月乙亥奉位版。妥侑如礼。而以书来请记。窃惟圣王之制祀典也。非徒先圣贤而已。凡有勋庸者。皆得与焉。故周官有司勋氏铭书祭烝之礼。尚书亦有纪功元祀之文。而记曰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能捍大患则祀之。今乙支公可谓御大菑捍大患。而死勤事劳定国。则其记功作祀而载之于司勋者。在所不已也。岂可以事在前代。而遂不崇报也。李公之意可谓美矣。而闵公之成其美者。尤见其公天下之善。而无间于人己也。抑又论之。当时以蕞尔属国。抗衡中夏。屠戮王师。困迫乘舆。以大失侯度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6L 页
 焉。则其时隋史必书以繻葛之法矣。然彼杨广者弑父烝母。不容于覆载之间者也。苟有桓文之君。则虽海外之邦。犹当声罪致讨。显戮于秦雍之郊矣。况广自送其死于我境欤。公能以小邦羸卒。大衄凶锋。终使浪死一曲。发天下乱。而广之宗无遗类焉。则可谓大快人心。而公之功不徒御大菑捍大患于一小邦而已也。呜呼。公虽逖焉。而其精爽之可畏者。则必不随死而亡矣。周公告成王纪功宗曰。汝受命笃弼。安知公之不亡者。不助我王家捍外侮而壮王猷。如周公之训也。二公之意。其亦不在是耶欤。呜呼可悲也尔。庚戌仲秋。恩津宋时烈记。
焉。则其时隋史必书以繻葛之法矣。然彼杨广者弑父烝母。不容于覆载之间者也。苟有桓文之君。则虽海外之邦。犹当声罪致讨。显戮于秦雍之郊矣。况广自送其死于我境欤。公能以小邦羸卒。大衄凶锋。终使浪死一曲。发天下乱。而广之宗无遗类焉。则可谓大快人心。而公之功不徒御大菑捍大患于一小邦而已也。呜呼。公虽逖焉。而其精爽之可畏者。则必不随死而亡矣。周公告成王纪功宗曰。汝受命笃弼。安知公之不亡者。不助我王家捍外侮而壮王猷。如周公之训也。二公之意。其亦不在是耶欤。呜呼可悲也尔。庚戌仲秋。恩津宋时烈记。砺山郡皇华亭记
皇华亭者。不知作于何时。世传古世华使之来。或由南海。北登旱路。此盖止宿供亿之所云尔。按舆地胜览亭在砺山郡北十一里。夫舆地之作。在于 成化年间。而斯亭见载则其后废坏。又不知在于何时尔。岂或燬于壬辰倭乱之日乎。今 上十年冬。郑侯采和来视郡事。不暇及他。而首复其亭。古诗所谓未到亭中名已好者。似为今日准备者也。亭凡三架。背震面兑。当两湖之交。形势俱焉。今则只为湖南按使交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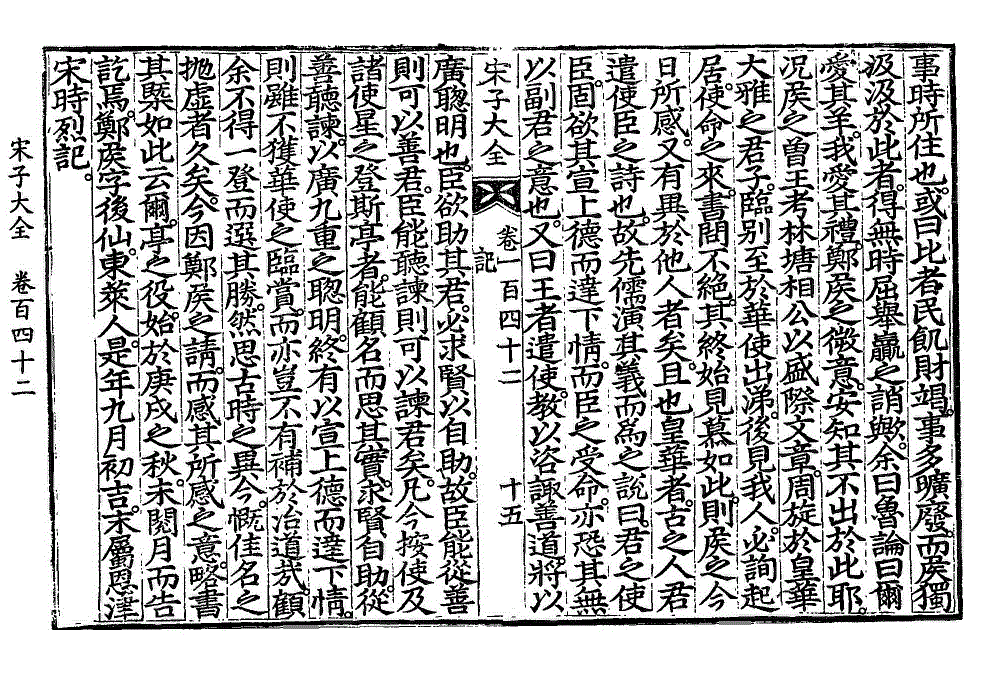 事时所住也。或曰比者民饥财竭。事多旷废。而侯独汲汲于此者。得无时屈举赢之诮欤。余曰鲁论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郑侯之微意。安知其不出于此耶。况侯之曾王考林塘相公以盛际文章。周旋于皇华大雅之君子。临别至于华使出涕。后见我人。必询起居。使命之来。书问不绝。其终始见慕如此。则侯之今日所感。又有异于他人者矣。且也皇华者。古之人君遣使臣之诗也。故先儒演其义而为之说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达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又曰王者遣使。教以咨诹善道。将以广聪明也。臣欲助其君。必求贤以自助。故臣能从善则可以善君。臣能听谏则可以谏君矣。凡今按使及诸使星之登斯亭者。能顾名而思其实。求贤自助。从善听谏。以广九重之聪明。终有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则虽不获华使之临赏。而亦岂不有补于治道哉。顾余不得一登而选其胜。然思古时之异今。慨佳名之抛虚者久矣。今因郑侯之请。而感其所感之意。略书其槩如此云尔。亭之役。始于庚戌之秋。未阅月而告讫焉。郑侯字后仙。东莱人。是年九月初吉。末属恩津宋时烈记。
事时所住也。或曰比者民饥财竭。事多旷废。而侯独汲汲于此者。得无时屈举赢之诮欤。余曰鲁论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郑侯之微意。安知其不出于此耶。况侯之曾王考林塘相公以盛际文章。周旋于皇华大雅之君子。临别至于华使出涕。后见我人。必询起居。使命之来。书问不绝。其终始见慕如此。则侯之今日所感。又有异于他人者矣。且也皇华者。古之人君遣使臣之诗也。故先儒演其义而为之说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达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恐其无以副君之意也。又曰王者遣使。教以咨诹善道。将以广聪明也。臣欲助其君。必求贤以自助。故臣能从善则可以善君。臣能听谏则可以谏君矣。凡今按使及诸使星之登斯亭者。能顾名而思其实。求贤自助。从善听谏。以广九重之聪明。终有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则虽不获华使之临赏。而亦岂不有补于治道哉。顾余不得一登而选其胜。然思古时之异今。慨佳名之抛虚者久矣。今因郑侯之请。而感其所感之意。略书其槩如此云尔。亭之役。始于庚戌之秋。未阅月而告讫焉。郑侯字后仙。东莱人。是年九月初吉。末属恩津宋时烈记。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7L 页
 镇川崔氏墓祭记
镇川崔氏墓祭记祖先之于子孙。虽年代悠远。如木之自根而干。自干而枝。则其实一而已矣。然贵贱有等。享祀不同。故士夫所祭世数。古今有异。而子朱子既定四代之礼。则士夫家无不遵用之矣。然人寿无多。更代频仍。则所谓五世即迁者。不过百来年间事矣。而孝子慈孙之心则不翅如朝暮之易过矣。故子朱子又以为分虽有限。而情则无穷也。遂定为中制。使于五世去庙之后。仍存墓祭。得以每岁一荐。而百世不改。其所以通幽明之故。厚人民之德者。可谓至矣。东俗例于正朝寒食端午秋夕。必上墓行盛祭。及至亲尽之后。则更不展省者多矣。以故失其坟墓所在者。往往而有焉。是不知朱子定制之意也。镇川有崔氏。旧为簪缨家。近岁考證朱子书。率其族人。以每岁孟冬。荐祀于远祖监务公之墓。监务公讳士兴。以孝行旌闾。其墓下外裔亦许参拜。骊兴闵进士泰重士昂亦其外裔之一也。尝来谓余曰。吾外氏奉先之仪。可谓美矣。然窃恐子孙不能遵奉。则将未免废坠于久远。盍为一言以警之乎。余谓墓祭古所未有。而起于乡俗。故南轩尝欲罢之。而朱子以人情之不可已者。往复论辨。然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8H 页
 后南轩亦悟前见之非。而烂熳同归。夫既以尊卑之有限。据世数去庙。而又废一祭于其墓。则子孙报本追远之诚。于何所寓焉。而其所谓根与干枝之为一者。断截而不续矣。吾未见截其根而枝干独存者矣。其能有其身难矣。于何以(以恐而)更责其奉先之礼乎。愿士昂只以朱子所制之礼。讲明其理于崔氏之后生。则将不患其不如今日之美矣。士昂以为如何。时 崇祯庚戌九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后南轩亦悟前见之非。而烂熳同归。夫既以尊卑之有限。据世数去庙。而又废一祭于其墓。则子孙报本追远之诚。于何所寓焉。而其所谓根与干枝之为一者。断截而不续矣。吾未见截其根而枝干独存者矣。其能有其身难矣。于何以(以恐而)更责其奉先之礼乎。愿士昂只以朱子所制之礼。讲明其理于崔氏之后生。则将不患其不如今日之美矣。士昂以为如何。时 崇祯庚戌九月日。恩津宋时烈记。游大冶山记
余来住华阳已六年矣。饱闻大冶之胜。大冶是仙游洞主山。而亦华阳之祖宗。去华阳十五里而近也。每岁一二番例赏仙游。而未尝一登兹山。真所谓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者也。顷者闻族人今大兴宰李最晚。与人说华阳仙游傍近有奇绝处。亦可以避世。因略道其形势云。乍闻直使人飘然有遗世之志。亟谂于往来村人。则无能知者。余以为此中可观处。余寻探殆遍。而未曾见如此者。居人亦未之知。则未知山水奇绝处。亦如幽人逸民晦迹藏踪于城市间。而世无能知者耶。然余于此间诸山。唯大冶独未寻到。无乃大兴所言只在此山之中耶。大兴以京洛贵游。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8L 页
 偶过而得见焉。则无乃天悭地秘者。将有意于见发也耶。遂以书问于大兴。而余以阙食之故。西归之期日迫。而又数日来雪霁风和。忽有剡溪之兴。遂以书邀辛生得中。盖辛生庄舍在大冶之前。而往来甚数。欲使为主人也。今月初三日。辛生自清安至。遂令先往。津遣僮马。初四日辛生遣三马一牛来。遂使殷,畴,淳,晦四孙先往。而吾则翌日早发。至草堂前。将渡溪水。则李君后望子久自武陵与其庶舅黄逵追至。余所带奴及从行古阜人金峻器布沙于岸冰而渡。黄,李则由石出处跳过。至巴谷上下渡则岸冰仅数尺广。马皆平渡。至辛庄前。招辛及四孙而与李先行。李谓先至普德庵。与僧辈谋登览也。遂向南沿溪而行。几十里许。子久曰普德不如是之远。恐是失路。止辔徘徊之际。忽有自后呼之者曰误行矣。遂笑而回辔。则辛生迎来。既至普德。则四孙先至而出迎矣。海州崔生慎自会宁。南阳洪生可相自安东。草溪卞生东佐自清州飞鸿。来在华阳书斋。而昨日亦已与四孙来待矣。少憩于寺前泉石。遂乘马指毗卢峰而行。毗卢峰者。乃大冶之上峰也。过数百步许。路险去马理策。僧辈以篮舆随行。而山麓峻急。不可乘矣。行数里
偶过而得见焉。则无乃天悭地秘者。将有意于见发也耶。遂以书问于大兴。而余以阙食之故。西归之期日迫。而又数日来雪霁风和。忽有剡溪之兴。遂以书邀辛生得中。盖辛生庄舍在大冶之前。而往来甚数。欲使为主人也。今月初三日。辛生自清安至。遂令先往。津遣僮马。初四日辛生遣三马一牛来。遂使殷,畴,淳,晦四孙先往。而吾则翌日早发。至草堂前。将渡溪水。则李君后望子久自武陵与其庶舅黄逵追至。余所带奴及从行古阜人金峻器布沙于岸冰而渡。黄,李则由石出处跳过。至巴谷上下渡则岸冰仅数尺广。马皆平渡。至辛庄前。招辛及四孙而与李先行。李谓先至普德庵。与僧辈谋登览也。遂向南沿溪而行。几十里许。子久曰普德不如是之远。恐是失路。止辔徘徊之际。忽有自后呼之者曰误行矣。遂笑而回辔。则辛生迎来。既至普德。则四孙先至而出迎矣。海州崔生慎自会宁。南阳洪生可相自安东。草溪卞生东佐自清州飞鸿。来在华阳书斋。而昨日亦已与四孙来待矣。少憩于寺前泉石。遂乘马指毗卢峰而行。毗卢峰者。乃大冶之上峰也。过数百步许。路险去马理策。僧辈以篮舆随行。而山麓峻急。不可乘矣。行数里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9H 页
 许。得至峰下。则绝壁干云。冰瀑垂崖。真奇观也。至路穷处。黄逵与一山氓先已缘壁度危。在半腰俯语曰。难矣。吾与少辈朋息仰望曰。危不可上矣。不如从此回归矣。或言到此而止则前功尽弃矣。且势甚峻截。终能至颠则当快心目矣。况黄亦非飞鸟而已能上去耶。黄遂以一条麻索垂下曰。试可缘此而上也。诸少之捷者。皆跻攀曰不至甚难矣。余亦从之。既上一层则又有一层而尤难。遂复缘索而上。盖二层之间。一石圆滑。无著足处。而俯临绝壑。心神𢥠然矣。黄又先行数十步。至回磴处曰。旧有栈以度矣。今已无之。度之甚危矣。或曰犹不如下二层之危矣。遂复以索挂于石罅小木。缘索悬空而度。从此始有丛林。穿林而上者几数百步。转折而南则忽见巨壁开坼作门。势甚奇壮。而俗离诸山罗列眼前矣。稍下数十步。又稍转而东。得毗卢庵故址。其安稳奇绝。不可形言。直可以旁日月凌风雨也。黄言有高僧义天筑庵于此。休粮而居者数年矣。既去而庵亦燬云。余忽自念人生一世。疾于转眄矣。奈何汩没尘间。不得处此清旷之界耶。朱先生晦庵在芦山绝顶。上下之际。有七颠八倒之语。则其绝险当不止此矣。盖绝险故人事罕
许。得至峰下。则绝壁干云。冰瀑垂崖。真奇观也。至路穷处。黄逵与一山氓先已缘壁度危。在半腰俯语曰。难矣。吾与少辈朋息仰望曰。危不可上矣。不如从此回归矣。或言到此而止则前功尽弃矣。且势甚峻截。终能至颠则当快心目矣。况黄亦非飞鸟而已能上去耶。黄遂以一条麻索垂下曰。试可缘此而上也。诸少之捷者。皆跻攀曰不至甚难矣。余亦从之。既上一层则又有一层而尤难。遂复缘索而上。盖二层之间。一石圆滑。无著足处。而俯临绝壑。心神𢥠然矣。黄又先行数十步。至回磴处曰。旧有栈以度矣。今已无之。度之甚危矣。或曰犹不如下二层之危矣。遂复以索挂于石罅小木。缘索悬空而度。从此始有丛林。穿林而上者几数百步。转折而南则忽见巨壁开坼作门。势甚奇壮。而俗离诸山罗列眼前矣。稍下数十步。又稍转而东。得毗卢庵故址。其安稳奇绝。不可形言。直可以旁日月凌风雨也。黄言有高僧义天筑庵于此。休粮而居者数年矣。既去而庵亦燬云。余忽自念人生一世。疾于转眄矣。奈何汩没尘间。不得处此清旷之界耶。朱先生晦庵在芦山绝顶。上下之际。有七颠八倒之语。则其绝险当不止此矣。盖绝险故人事罕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59L 页
 至。而可以静坐观书矣。如以口腹为难。则蔡先生登西山。只啖荠度日。只在人立志之如何矣。余欲于此结茅。悉取书册而藏之。仍送馀日。不亦可乎。而精神已耗。不可自力矣。同志之士。其有能相助而成之者否。余自华阳。佩一壶来。登陟既多。思引一杯。问之则僧曰置在山腰矣。遂西步寻井泉。则水自岩窦而出者数处。遂捧饮数口。回寻石门而下。至回磴及二层则其垂下之难。甚于扳登时。然顷刻之间。已到乎迤逦处矣。辛生始不从矣。自普德持柹梨一器及松茸一碗和蜜者则如新采矣。而余所佩一壶亦在矣。与诸少共之。快美难状也。遂咏朱先生朗吟飞下祝融峰之句。回到普德则日已暮。辛生已令寺僧具饭。既而归华阳则几人定矣。畴孙到巴谷滨。马惊惊湍而堕。终夜呻吟。盖事未易全胜者也。夜卧回思则恍然一梦瑶台矣。因念自人世言之。则此华阳者可谓仙境。而视毗卢则又是尘世趣象也。岂独地界为然。人之地位愈高则其所见愈异矣。吾辈于外面地界。犹不得处于穷极处。则况其他又可论耶。亦可为少而不力者之戒也。庚戌十一月初六日。华阳洞主人记。
至。而可以静坐观书矣。如以口腹为难。则蔡先生登西山。只啖荠度日。只在人立志之如何矣。余欲于此结茅。悉取书册而藏之。仍送馀日。不亦可乎。而精神已耗。不可自力矣。同志之士。其有能相助而成之者否。余自华阳。佩一壶来。登陟既多。思引一杯。问之则僧曰置在山腰矣。遂西步寻井泉。则水自岩窦而出者数处。遂捧饮数口。回寻石门而下。至回磴及二层则其垂下之难。甚于扳登时。然顷刻之间。已到乎迤逦处矣。辛生始不从矣。自普德持柹梨一器及松茸一碗和蜜者则如新采矣。而余所佩一壶亦在矣。与诸少共之。快美难状也。遂咏朱先生朗吟飞下祝融峰之句。回到普德则日已暮。辛生已令寺僧具饭。既而归华阳则几人定矣。畴孙到巴谷滨。马惊惊湍而堕。终夜呻吟。盖事未易全胜者也。夜卧回思则恍然一梦瑶台矣。因念自人世言之。则此华阳者可谓仙境。而视毗卢则又是尘世趣象也。岂独地界为然。人之地位愈高则其所见愈异矣。吾辈于外面地界。犹不得处于穷极处。则况其他又可论耶。亦可为少而不力者之戒也。庚戌十一月初六日。华阳洞主人记。清州青川社仓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0H 页
 岁在 崇祯庚戌。国内大饥。民人死者十而六七。时岭南按使李公䎘仲羽。竭诚赈恤。以活全岭。余时在清州青川县之华阳。实与岭相接。每闻其勤恤。为岭人庆也。公以余枵腹空山。亦一王民之可怜者。以俸馀米在闻庆者十斛。帖本县输送。时 显宗大王已轸 圣虑。别有周急之恩。其于 恩赐。亦当免死而已。况添以此米。则义实有所难安矣。遂以此请辞则公曰虽然勿外也。余犹以自遂为期。而公已递归矣。庆县复输送曰。前政去时。有所申命。敢以为请。余以为公之诚则诚有所难孤也。而余之狷滞。亦有难猝化者。然但思自安之道。而不思庆县所处之难。则又非平物我之心也。适大学士李公端夏请行朱子社仓法于诸道。以备水旱。 上即允之。而其事颁下。余曰吾知所以处此矣。昔朱先生及魏艮斋之为社仓也。皆请米于府官与使者以为本。而岁贷收息。所息侔本则还其本于官矣。今者以此米为本。则无复官米之请。而且无责还之虞矣。遂与金得泗,辛得中,洪胄炳等相议。募民之愿入者。则尚州,闻庆,槐山之犬牙于青川者。颇有喜闻者焉。遂各出若干谷。以补于原米。而其敛散之规。一依朱先生所定。则李公之惠
岁在 崇祯庚戌。国内大饥。民人死者十而六七。时岭南按使李公䎘仲羽。竭诚赈恤。以活全岭。余时在清州青川县之华阳。实与岭相接。每闻其勤恤。为岭人庆也。公以余枵腹空山。亦一王民之可怜者。以俸馀米在闻庆者十斛。帖本县输送。时 显宗大王已轸 圣虑。别有周急之恩。其于 恩赐。亦当免死而已。况添以此米。则义实有所难安矣。遂以此请辞则公曰虽然勿外也。余犹以自遂为期。而公已递归矣。庆县复输送曰。前政去时。有所申命。敢以为请。余以为公之诚则诚有所难孤也。而余之狷滞。亦有难猝化者。然但思自安之道。而不思庆县所处之难。则又非平物我之心也。适大学士李公端夏请行朱子社仓法于诸道。以备水旱。 上即允之。而其事颁下。余曰吾知所以处此矣。昔朱先生及魏艮斋之为社仓也。皆请米于府官与使者以为本。而岁贷收息。所息侔本则还其本于官矣。今者以此米为本。则无复官米之请。而且无责还之虞矣。遂与金得泗,辛得中,洪胄炳等相议。募民之愿入者。则尚州,闻庆,槐山之犬牙于青川者。颇有喜闻者焉。遂各出若干谷。以补于原米。而其敛散之规。一依朱先生所定。则李公之惠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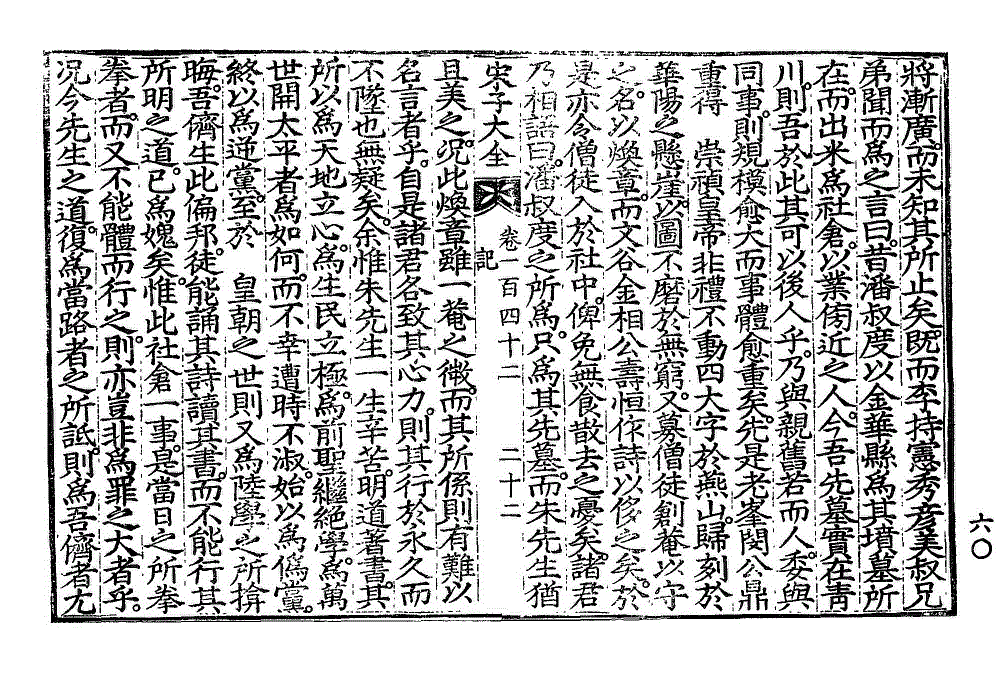 将渐广。而未知其所止矣。既而李持宪秀彦,美叔兄弟闻而为之言曰。昔潘叔度以金华县为其坟墓所在。而出米为社仓。以业傍近之人。今吾先墓实在青川。则吾于此其可以后人乎。乃与亲旧若而人。委与同事。则规模愈大而事体愈重矣。先是老峰闵公鼎重得 崇祯皇帝非礼不动四大字于燕山。归刻于华阳之悬崖。以图不磨于无穷。又募僧徒创庵以守之。名以焕章。而文谷金相公寿恒作诗以侈之矣。于是亦令僧徒入于社中。俾免无食散去之忧矣。诸君乃相语曰。潘叔度之所为。只为其先墓。而朱先生犹且美之。况此焕章虽一庵之微。而其所系则有难以名言者乎。自是诸君各致其心力。则其行于永久而不坠也无疑矣。余惟朱先生一生辛苦。明道著书。其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为如何。而不幸遭时不淑。始以为伪党。终以为逆党。至于 皇朝之世则又为陆学之所掩晦。吾侪生此偏邦。徒能诵其诗读其书。而不能行其所明之道。已为愧矣。惟此社仓一事。是当日之所拳拳者。而又不能体而行之。则亦岂非为罪之大者乎。况今先生之道。复为当路者之所诋。则为吾侪者尤
将渐广。而未知其所止矣。既而李持宪秀彦,美叔兄弟闻而为之言曰。昔潘叔度以金华县为其坟墓所在。而出米为社仓。以业傍近之人。今吾先墓实在青川。则吾于此其可以后人乎。乃与亲旧若而人。委与同事。则规模愈大而事体愈重矣。先是老峰闵公鼎重得 崇祯皇帝非礼不动四大字于燕山。归刻于华阳之悬崖。以图不磨于无穷。又募僧徒创庵以守之。名以焕章。而文谷金相公寿恒作诗以侈之矣。于是亦令僧徒入于社中。俾免无食散去之忧矣。诸君乃相语曰。潘叔度之所为。只为其先墓。而朱先生犹且美之。况此焕章虽一庵之微。而其所系则有难以名言者乎。自是诸君各致其心力。则其行于永久而不坠也无疑矣。余惟朱先生一生辛苦。明道著书。其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为如何。而不幸遭时不淑。始以为伪党。终以为逆党。至于 皇朝之世则又为陆学之所掩晦。吾侪生此偏邦。徒能诵其诗读其书。而不能行其所明之道。已为愧矣。惟此社仓一事。是当日之所拳拳者。而又不能体而行之。则亦岂非为罪之大者乎。况今先生之道。复为当路者之所诋。则为吾侪者尤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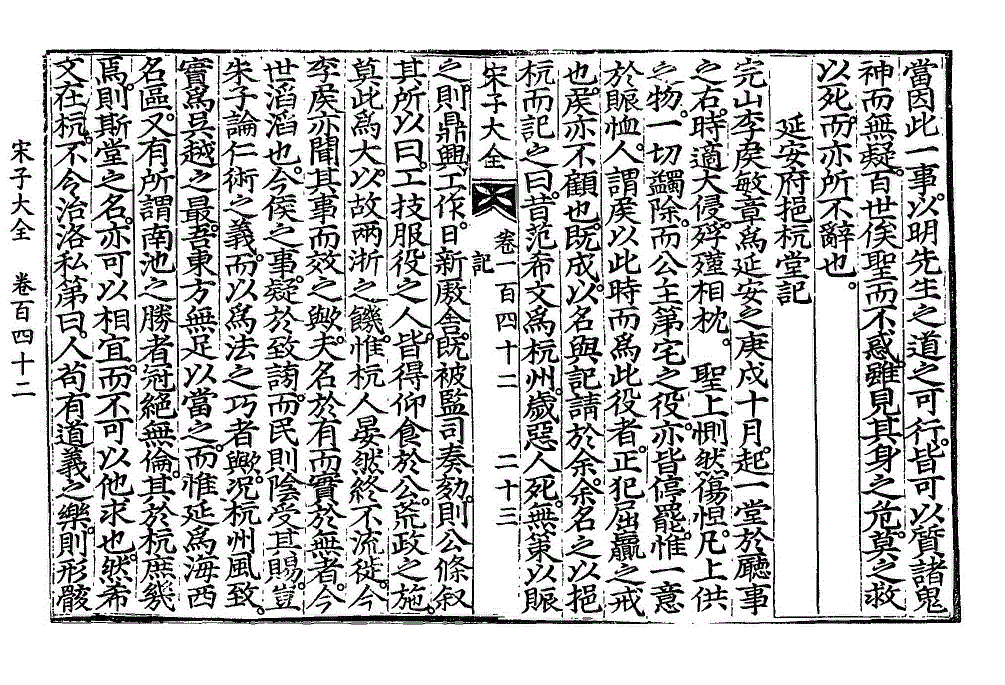 当因此一事。以明先生之道之可行。皆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俟圣而不惑。虽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而亦所不辞也。
当因此一事。以明先生之道之可行。皆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俟圣而不惑。虽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而亦所不辞也。延安府挹杭堂记
完山李侯敏章为延安之庚戌十月。起一堂于厅事之右。时适大侵。殍殣相枕。 圣上恻然伤怛。凡上供之物。一切蠲除。而公主第宅之役。亦皆停罢。惟一意于赈恤。人谓侯以此时而为此役者。正犯屈赢之戒也。侯亦不顾也。既成。以名与记请于余。余名之以挹杭而记之曰。昔范希文为杭州。岁恶人死。无策以赈之。则鼎兴工作。日新廒舍。既被监司奏劾。则公条叙其所以曰。工技服役之人。皆得仰食于公。荒政之施。莫此为大。以故两浙之饥。惟杭人晏然终不流徙。今李侯亦闻其事而效之欤。夫名于有而实于无者。今世滔滔也。今侯之事。疑于致谤。而民则阴受其赐。岂朱子论仁术之义。而以为法之巧者欤。况杭州风致。实为吴越之最。吾东方无足以当之。而惟延为海西名区。又有所谓南池之胜者冠绝无伦。其于杭庶几焉。则斯堂之名。亦可以相宜。而不可以他求也。然希文在杭。不令治洛私第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则形骸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1L 页
 亦可外焉。又况居第乎哉。且洛阳士大夫园林相望。而主人者莫得常游。谁得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吾乐哉。今侯有先庐数架于白马江上。而不曾修治。独于斯堂而致意若是。亦所以慕希文杭州之志也欤。凡后之登斯堂者。既知希文恤民之仁。而又知其不营己私之心。则可以遗外物欲。独观昭旷之原。彼之朱栏曲槛。皆不足以婴吾心。而可进于先忧后乐之地矣。故吾僭为之说。而以告后之观者焉。翌年重光大渊献仲春日。恩津宋时烈记。
亦可外焉。又况居第乎哉。且洛阳士大夫园林相望。而主人者莫得常游。谁得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吾乐哉。今侯有先庐数架于白马江上。而不曾修治。独于斯堂而致意若是。亦所以慕希文杭州之志也欤。凡后之登斯堂者。既知希文恤民之仁。而又知其不营己私之心。则可以遗外物欲。独观昭旷之原。彼之朱栏曲槛。皆不足以婴吾心。而可进于先忧后乐之地矣。故吾僭为之说。而以告后之观者焉。翌年重光大渊献仲春日。恩津宋时烈记。净友堂后记
余尝为金延之记净友堂事。而颇用濂翁爱莲说矣。后十馀年。堂既无有。而完山李侯晋子明稍移故址而新之。其规制亦非旧观矣。夫延之之爱。不敢谓遽同于濂翁。而延之,子明之爱则可谓同矣。同二君之爱者。继而来则斯亭庶几不坏矣。
九四堂记
清阴先生自少以小学律身。而其学专主于敬。真得为学之要。故其操而存之日益固。扩而充之日益远。其所成就。终至于轩天地曜日月而无穷也。呜呼盛哉。然其所谓敬者。非别为一物。只在于正容体顺辞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2H 页
 令。端庄齐肃之间也。戴记所谓九容。论语所谓四勿者。即其事也。先生一生之所受用者。专在于兹。尝于丁丑乱后。遁于丰山。为书其目。以赐其第三孙今冢宰公寿恒。冢宰公罔敢失坠。遂构堂而揭以九四之名。将朝夕寓目而警省焉曰。其敢不夙兴夜寐。毋或不虔。以忝先训。呜呼。先生之为祖。冢宰之为孙。其可谓得授受之要旨矣。呜呼。圣贤之书。士谁有不读者。然知要守约。深思力行者寡矣。夫四勿者。夫子以斯道之传。传之颜子之妙诀。则无以尚之。而至于九容者则又晦翁夫子特举之以答请读何书之问。而又戒其昧此者之为大奸慝。圣贤心法。亦无以易此也。今以此二者。合而为一。外以治身。内以治心。内外交养。无少间断。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况先生当其大乱之馀。栖遑南裔。冢宰亦童羁东表之日。而乃以此相勉。则岂非朝闻夕死之志。炯然可见。而其付托之重。独眷眷于冢宰者。亦岂以门人知旧无可以受此者欤。其微意亦可以默识矣。呜呼。冢宰其可不没身而服膺之哉。时 崇祯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令。端庄齐肃之间也。戴记所谓九容。论语所谓四勿者。即其事也。先生一生之所受用者。专在于兹。尝于丁丑乱后。遁于丰山。为书其目。以赐其第三孙今冢宰公寿恒。冢宰公罔敢失坠。遂构堂而揭以九四之名。将朝夕寓目而警省焉曰。其敢不夙兴夜寐。毋或不虔。以忝先训。呜呼。先生之为祖。冢宰之为孙。其可谓得授受之要旨矣。呜呼。圣贤之书。士谁有不读者。然知要守约。深思力行者寡矣。夫四勿者。夫子以斯道之传。传之颜子之妙诀。则无以尚之。而至于九容者则又晦翁夫子特举之以答请读何书之问。而又戒其昧此者之为大奸慝。圣贤心法。亦无以易此也。今以此二者。合而为一。外以治身。内以治心。内外交养。无少间断。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况先生当其大乱之馀。栖遑南裔。冢宰亦童羁东表之日。而乃以此相勉。则岂非朝闻夕死之志。炯然可见。而其付托之重。独眷眷于冢宰者。亦岂以门人知旧无可以受此者欤。其微意亦可以默识矣。呜呼。冢宰其可不没身而服膺之哉。时 崇祯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谷云精舍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2L 页
 安东金延之为平康县。一日忽起孙公赤城之兴。屏徒隶。或涉或登。行数百里。竟至春川之史吞。其幽深夐阻之势。清旷静寂之趣。有不可名状者。其中奇绝之处。名号朴陋。皆有以换之。遂有傍花雪云二溪。水云悦云二台。神女峡笼水亭卧龙潭归云洞。则有如西子之蒙不洁。而一朝洗濯于清泠之渊也。溪山涧谷。不可谓不遇矣。而自见遇者言之。数十里之间。经略布置。大纲小维。尽为吾物外之藏矣。村居滴历。吠烟不相连属。而有官仓积粟。所以粜籴于村民者也。有村民指一颓址曰。此相传以为五岁童子之基。盖梅月金公生才数月。自能知书。至五岁则于经传子史。无不通贯。故当时目以五岁。而至其长大。犹以是称之。事俱载野史诸书。 世祖朝托迹缁流。放情丘壑。秽貊之墟。瓶锡殆遍。此其尝为栖息之地也欤。公作诗甚多。喜使薇蕨字。故今又改其谷曰采薇。而将作一间精舍。名以谷云。置公像其间。与村老樵夫。酌飞泉以侑之而未暇也。然已结数椽茅舍。以为早晚归休之所。则是将为次第事矣。盖公之踪迹。人或不欲深言者矣。至我 宣庙朝。栗谷先生承命立传以进之。则自后人人公诵之。至于湖西之鸿山。是公毕
安东金延之为平康县。一日忽起孙公赤城之兴。屏徒隶。或涉或登。行数百里。竟至春川之史吞。其幽深夐阻之势。清旷静寂之趣。有不可名状者。其中奇绝之处。名号朴陋。皆有以换之。遂有傍花雪云二溪。水云悦云二台。神女峡笼水亭卧龙潭归云洞。则有如西子之蒙不洁。而一朝洗濯于清泠之渊也。溪山涧谷。不可谓不遇矣。而自见遇者言之。数十里之间。经略布置。大纲小维。尽为吾物外之藏矣。村居滴历。吠烟不相连属。而有官仓积粟。所以粜籴于村民者也。有村民指一颓址曰。此相传以为五岁童子之基。盖梅月金公生才数月。自能知书。至五岁则于经传子史。无不通贯。故当时目以五岁。而至其长大。犹以是称之。事俱载野史诸书。 世祖朝托迹缁流。放情丘壑。秽貊之墟。瓶锡殆遍。此其尝为栖息之地也欤。公作诗甚多。喜使薇蕨字。故今又改其谷曰采薇。而将作一间精舍。名以谷云。置公像其间。与村老樵夫。酌飞泉以侑之而未暇也。然已结数椽茅舍。以为早晚归休之所。则是将为次第事矣。盖公之踪迹。人或不欲深言者矣。至我 宣庙朝。栗谷先生承命立传以进之。则自后人人公诵之。至于湖西之鸿山。是公毕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3H 页
 命之所。故章甫之徒立祠以祀之。盖曰泰伯断发文身。而其崇报之祠在吴中。至唐狄梁公焚灭千馀祠。而此独岿然。则其义一揆也。于是延之喟然叹曰。吾东山水。以蓬莱之万瀑为第一。而若其水石平旷。洞府宽广。可以游泳盘旋而栖止耕凿者。则彼将有所逊焉。而况有梅月之遗迹。则吾之占之为依归之所。乌可已乎。遂驰书问记于余。余曰显晦者理也。迟速者时也。今此史吞者。自其峙流以来。历几千万年。而始为梅月公之所游赏。又并梅月公埋没者复几年。而再发于延之。从今以往。吾将期其有显。而长永无晦也。盖其发之迟者。传之常久也。余仍有所告于延之者。延之既以卧龙名潭。则晦翁庐山之举。将不仿而为之乎。吾欲为延之之西原子虚。而老矣不可得矣。遂书晦翁诗以贻之。如后万一有成则愿以此揭之壁间也。延之名寿增。清阴先生之嗣孙也。时 崇祯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命之所。故章甫之徒立祠以祀之。盖曰泰伯断发文身。而其崇报之祠在吴中。至唐狄梁公焚灭千馀祠。而此独岿然。则其义一揆也。于是延之喟然叹曰。吾东山水。以蓬莱之万瀑为第一。而若其水石平旷。洞府宽广。可以游泳盘旋而栖止耕凿者。则彼将有所逊焉。而况有梅月之遗迹。则吾之占之为依归之所。乌可已乎。遂驰书问记于余。余曰显晦者理也。迟速者时也。今此史吞者。自其峙流以来。历几千万年。而始为梅月公之所游赏。又并梅月公埋没者复几年。而再发于延之。从今以往。吾将期其有显。而长永无晦也。盖其发之迟者。传之常久也。余仍有所告于延之者。延之既以卧龙名潭。则晦翁庐山之举。将不仿而为之乎。吾欲为延之之西原子虚。而老矣不可得矣。遂书晦翁诗以贻之。如后万一有成则愿以此揭之壁间也。延之名寿增。清阴先生之嗣孙也。时 崇祯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沃川郡去思堂记
沃之为郡。地旷民贫。长民者或失其人。则辄有捐瘠之忧。岁在 崇祯纪元之戊申。沈侯攸辍从班来莅焉。侯以名家良子弟。其风度已著于未至之时。既周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3L 页
 一载。为政之善。不可胜记。盖不甚综理。而惟以清省自喜。其所施为。则简节疏目。谈笑于簿领。而吏民无不自得焉。故人无不称善。而或问其所为之善。则亦无以切切言之者矣。盖既去而民益思之。先是朝廷以为为吏者类多违道干誉。而民之颂之者。亦诚伪相半。遂颁新令。以严立碑之禁。沃民无以寓其怀。则相与揭刻于治西断麓之石崖。行路观之。无不耸目。今年辛亥。南原尹侯衡圣亦自迩列。隔一手来奠其民。见沈侯所搆小屋在客舍西偏之十许步。而功犹未毕。侯遂讫其涂塈。而默察一郡之情愿。名曰去思。盖亦崖刻之意也。余惟善者。天下之公理也。然人惟有私意也。故人有善好之者常少。而其不好之者常多。况守宰于前人则其不指瑕疵者亦鲜矣。又可望其称道之耶。故闻人之誉之者则刚者未尝不怒于言。懦者未尝不怒于色。而有毁之者则亦随其刚懦而言色之悦必见焉。今侯之所为如此。则沈侯之善。即侯之善也。故其革旧弊宽民隐。律己束吏。杜私奉公。已使邻并承楷。其政虽不尽同于沈侯。而其心之善。未尝不同也。然侯以年老。指鬓毛而已有赋归之意。郡人之忧思深矣。则其既去之后。亦可知尔。然则
一载。为政之善。不可胜记。盖不甚综理。而惟以清省自喜。其所施为。则简节疏目。谈笑于簿领。而吏民无不自得焉。故人无不称善。而或问其所为之善。则亦无以切切言之者矣。盖既去而民益思之。先是朝廷以为为吏者类多违道干誉。而民之颂之者。亦诚伪相半。遂颁新令。以严立碑之禁。沃民无以寓其怀。则相与揭刻于治西断麓之石崖。行路观之。无不耸目。今年辛亥。南原尹侯衡圣亦自迩列。隔一手来奠其民。见沈侯所搆小屋在客舍西偏之十许步。而功犹未毕。侯遂讫其涂塈。而默察一郡之情愿。名曰去思。盖亦崖刻之意也。余惟善者。天下之公理也。然人惟有私意也。故人有善好之者常少。而其不好之者常多。况守宰于前人则其不指瑕疵者亦鲜矣。又可望其称道之耶。故闻人之誉之者则刚者未尝不怒于言。懦者未尝不怒于色。而有毁之者则亦随其刚懦而言色之悦必见焉。今侯之所为如此。则沈侯之善。即侯之善也。故其革旧弊宽民隐。律己束吏。杜私奉公。已使邻并承楷。其政虽不尽同于沈侯。而其心之善。未尝不同也。然侯以年老。指鬓毛而已有赋归之意。郡人之忧思深矣。则其既去之后。亦可知尔。然则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4H 页
 斯堂也。毕竟为何侯之堂也。噫。公天下之善。而破藩篱之障者。古道也。故朱夫子称之以大方。苟古道既复。而人无物我之私。则不独两侯为此堂之主。继而来而善于政者。皆可为主人。而此堂为一大公物矣。其所谓大方者。真在是矣。虽然至愚而神者民也。所为虽善。而苟有意于民之思我。则其浅小屈曲之态。随事彰露。而民反不思之矣。故南轩张子曰有所为而为之者利也。此虽与货财有异。而其为利心则一也。盖公私之岐于心者甚微。而向背之应于民者至著。可不惧哉。此又为政者之所当知也。时 崇祯辛亥十一月日。郡人宋时烈记。
斯堂也。毕竟为何侯之堂也。噫。公天下之善。而破藩篱之障者。古道也。故朱夫子称之以大方。苟古道既复。而人无物我之私。则不独两侯为此堂之主。继而来而善于政者。皆可为主人。而此堂为一大公物矣。其所谓大方者。真在是矣。虽然至愚而神者民也。所为虽善。而苟有意于民之思我。则其浅小屈曲之态。随事彰露。而民反不思之矣。故南轩张子曰有所为而为之者利也。此虽与货财有异。而其为利心则一也。盖公私之岐于心者甚微。而向背之应于民者至著。可不惧哉。此又为政者之所当知也。时 崇祯辛亥十一月日。郡人宋时烈记。天安郡明节亭记
古者执艺。莫先于射。射不惟以御乱。兼有以观德。故自天子以下。皆有乐以为节。其义深矣。大夫以采蘋为节者。乐循法也。士以采蘩为节者。乐不失职也。故记礼者曰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后世此道不讲。则无惑乎不循法失其职。而反度背规。喜惰好纵。使其国日趋于危亡也。昌宁曹侯为天安之七年。治其邑之射亭而新之。问名于余。余取记礼者之言。名以明节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4L 页
 而告之曰。夫射者。男子之事。而君子之所重。故自其始生而悬弧于门左。始负而以桑弧蓬矢。人为之射天地四方。既长而不能则辞以疾。而不敢言未习。则其不可不习也明矣。其习之之时。大夫而必明其循法之节。则法立而能守。事可久而业可大矣。为士而必明其不失职之节。则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而皆得为良士矣。如是则国事其庶几乎。昔召公戒康王初服。以为守成之世。多溺于宴安矣。苟不诘其戎兵。奋扬武烈。则陵迟之渐见矣。故必以张皇六师。为无坏其高祖寡命之本。而朱夫子尝备贼于同安也。自当贼冲。而一面作射圃于城隅。属其徒。日射其间而曰。必习于无事之时。然后缓急可赖也。夫康王之时。天下极治。而召公之戒如此。同安之日。贼势甚急。而朱子之事如此。然则安固不可谓事无足为。而危亦不可谓事无所及也。呜呼。本朝今日之势。可谓安耶危耶。宜乎曹侯赈饥掩殣。日不可暇给。而于此尤拳拳也。继而来者。能以曹侯之心为心。而不至于坠废。则邑中之士夫必将兴起。而自明其节。推而至于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无不各职其职而以明其节。则张子所谓朝廷大有所益者。其在是矣。而亦岂无明其大
而告之曰。夫射者。男子之事。而君子之所重。故自其始生而悬弧于门左。始负而以桑弧蓬矢。人为之射天地四方。既长而不能则辞以疾。而不敢言未习。则其不可不习也明矣。其习之之时。大夫而必明其循法之节。则法立而能守。事可久而业可大矣。为士而必明其不失职之节。则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而皆得为良士矣。如是则国事其庶几乎。昔召公戒康王初服。以为守成之世。多溺于宴安矣。苟不诘其戎兵。奋扬武烈。则陵迟之渐见矣。故必以张皇六师。为无坏其高祖寡命之本。而朱夫子尝备贼于同安也。自当贼冲。而一面作射圃于城隅。属其徒。日射其间而曰。必习于无事之时。然后缓急可赖也。夫康王之时。天下极治。而召公之戒如此。同安之日。贼势甚急。而朱子之事如此。然则安固不可谓事无足为。而危亦不可谓事无所及也。呜呼。本朝今日之势。可谓安耶危耶。宜乎曹侯赈饥掩殣。日不可暇给。而于此尤拳拳也。继而来者。能以曹侯之心为心。而不至于坠废。则邑中之士夫必将兴起。而自明其节。推而至于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无不各职其职而以明其节。则张子所谓朝廷大有所益者。其在是矣。而亦岂无明其大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5H 页
 节。而担当世道者。将出于此邑也。余将拱手而俟之矣。呜呼。余既以朱子事。略及于前矣。复以毕其说可乎。朱子于初到漳州之时。教习弓射。皆无一人能之者。遂作三番。每月轮入教场。弯弓及等者赏之。其不及者留之。只管弯射。终不及则罢之。两月之间。翕然都及上等。此岂非讲武之明法乎。今之为士者。耻言武事。抑何异欤。至于明节之义。则朱子与人言。所必称者。此不须云矣。曹侯名敬彬字华叔。昌宁人。壬子四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节。而担当世道者。将出于此邑也。余将拱手而俟之矣。呜呼。余既以朱子事。略及于前矣。复以毕其说可乎。朱子于初到漳州之时。教习弓射。皆无一人能之者。遂作三番。每月轮入教场。弯弓及等者赏之。其不及者留之。只管弯射。终不及则罢之。两月之间。翕然都及上等。此岂非讲武之明法乎。今之为士者。耻言武事。抑何异欤。至于明节之义。则朱子与人言。所必称者。此不须云矣。曹侯名敬彬字华叔。昌宁人。壬子四月日。恩津宋时烈记。任实县愧俸楼记
申侯圣时为县之数月。以赈恤之暇。治其贮财之廒。因辟其傍数架。以为登临治事之所。而间以书问名于余。余名以愧俸而告之曰。昔朱夫子之为吏也。每诵韦苏州道(道恐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夫夫子之为政。宜无所不至。而犹以此自诵。则后之为政者。尤岂可以不尽其心。而徒以哺啜为哉。侯以晨夕登斯楼也。远望街路。见其有保抱妇子。颠倒困顿之民。而吾乃列鼎排案。食有鱼肉。则其不能安于心而愧于颜也自不能已矣。不如是而但为所居之移。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而凡彼之痒疴疾痛。皆不能属己矣。仁人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5L 页
 心。乌可如是耶。第以徒有愧之之意。而不思所以无愧之道。则无益于民之捐瘠。而其为愧也终不去矣。必须以朱夫子忠厚恻怛之心为心。而其时措之宜条理之密。又必如夫子绍兴之荒政。然后可庶几矣。虽然夫子虽诵此句。而又必以故纵吏胥。畏惮权豪。为今仕宦者之病。而自不免追究人吏。监禁断遣之严。夫忠厚恻怛。固是为政之本。而纵吏胥惮权豪。必反害于忠厚恻怛之政矣。古人有言曰养稂莠者害嘉谷。然则为政之道。又须内外兼尽。刚柔相济。然后可以真无愧于俸钱矣。然后登斯楼而四望。则昔日之保抱颠顿者。举变为安堵乐业之民矣。如是则俸钱之厚。虽至于肥妻子饫僮仆。亦不为过矣。而虽复既去而徵吉贝。如夫子之为亦可也。圣时尝读书为儒。而最好朱夫子书。故终始以夫子说相告。圣时想乐闻而不逆于意矣。愚既以此相告。而于俸钱之说。复有所感焉。夫子生乎南渡之后。每感慨于诸葛丞相。故虽自言其诵韦诗。而因又言自用俸钱作卧龙庵于庐山之深谷而曰。神交付冥漠。今之为政者。虽使民饱食兴事。而苟无此意思。则亦何足观哉。是则终为愧俸之人矣。此尤不可不知也。圣时名启澄。高
心。乌可如是耶。第以徒有愧之之意。而不思所以无愧之道。则无益于民之捐瘠。而其为愧也终不去矣。必须以朱夫子忠厚恻怛之心为心。而其时措之宜条理之密。又必如夫子绍兴之荒政。然后可庶几矣。虽然夫子虽诵此句。而又必以故纵吏胥。畏惮权豪。为今仕宦者之病。而自不免追究人吏。监禁断遣之严。夫忠厚恻怛。固是为政之本。而纵吏胥惮权豪。必反害于忠厚恻怛之政矣。古人有言曰养稂莠者害嘉谷。然则为政之道。又须内外兼尽。刚柔相济。然后可以真无愧于俸钱矣。然后登斯楼而四望。则昔日之保抱颠顿者。举变为安堵乐业之民矣。如是则俸钱之厚。虽至于肥妻子饫僮仆。亦不为过矣。而虽复既去而徵吉贝。如夫子之为亦可也。圣时尝读书为儒。而最好朱夫子书。故终始以夫子说相告。圣时想乐闻而不逆于意矣。愚既以此相告。而于俸钱之说。复有所感焉。夫子生乎南渡之后。每感慨于诸葛丞相。故虽自言其诵韦诗。而因又言自用俸钱作卧龙庵于庐山之深谷而曰。神交付冥漠。今之为政者。虽使民饱食兴事。而苟无此意思。则亦何足观哉。是则终为愧俸之人矣。此尤不可不知也。圣时名启澄。高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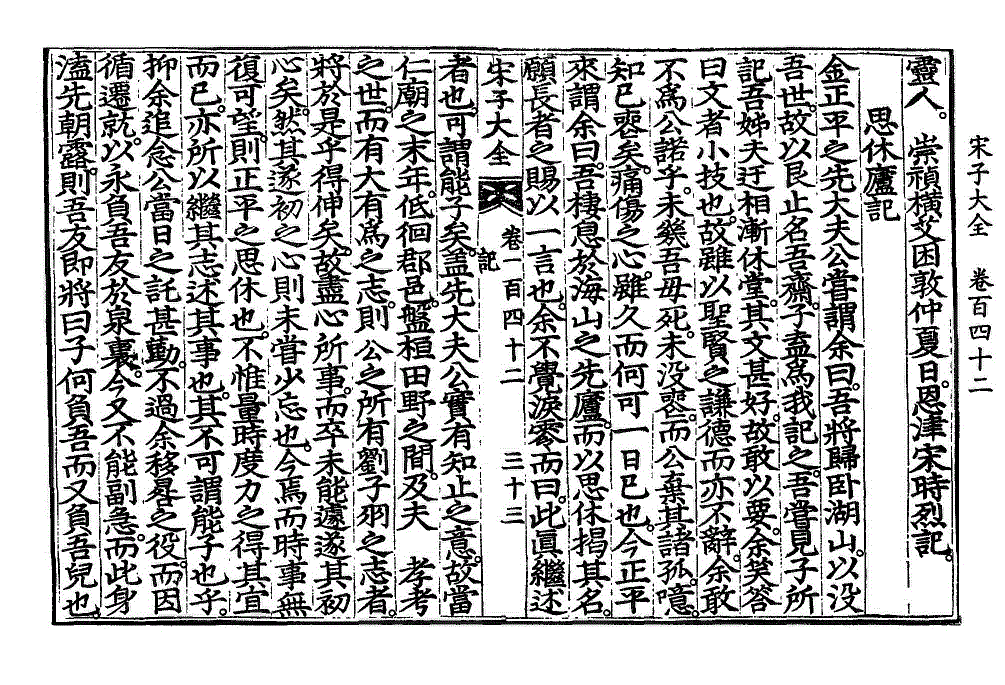 灵人。 崇祯横艾困敦仲夏日。恩津宋时烈记。
灵人。 崇祯横艾困敦仲夏日。恩津宋时烈记。思休庐记
金正平之先大夫公尝谓余曰。吾将归卧湖山。以没吾世。故以艮止名吾斋。子盍为我记之。吾尝见子所记吾姊夫迂相渐休堂。其文甚好。故敢以要。余笑答曰文者小技也。故虽以圣贤之谦德而亦不辞。余敢不为公诺乎。未几吾母死。未没丧。而公弃其诸孤。噫。知已丧矣。痛伤之心。虽久而何可一日已也。今正平来谓余曰。吾栖息于海山之先庐。而以思休揭其名。愿长者之赐以一言也。余不觉泪零而曰。此真继述者也。可谓能子矣。盖先大夫公实有知止之意。故当仁庙之末年。低徊郡邑。盘桓田野之间。及夫 孝考之世。而有大有为之志。则公之所有刘子羽之志者。将于是乎得伸矣。故尽心所事。而卒未能遽遂其初心矣。然其遂初之心则未尝少忘也。今焉而时事无复可望。则正平之思休也。不惟量时度力之得其宜而已。亦所以继其志述其事也。其不可谓能子也乎。抑余追念公当日之托甚勤。不过余移晷之役。而因循迁就。以永负吾友于泉里。今又不能副急。而此身溘先朝露。则吾友即将曰子何负吾而又负吾儿也。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6L 页
 故急起呼烛而书之如此。盖艮为止。而休亦止之之意也。然则今余虽记思休。而其实亦所以记艮止也。然则余虽负于前。而尚可以赎于后矣。因亦思渐休公而重为掩涕也。虽然思者。将然而未然之辞也。岂正平自以为吾以乔木世臣。儒臣后承。当此王室存亡之秋。何忍遽决其去就也云。故犹有商量迟疑耶。然则其心亦可谓戚矣。未知正平之意其果然乎。 崇祯横艾困敦季夏十二日。华阳老叟书。
故急起呼烛而书之如此。盖艮为止。而休亦止之之意也。然则今余虽记思休。而其实亦所以记艮止也。然则余虽负于前。而尚可以赎于后矣。因亦思渐休公而重为掩涕也。虽然思者。将然而未然之辞也。岂正平自以为吾以乔木世臣。儒臣后承。当此王室存亡之秋。何忍遽决其去就也云。故犹有商量迟疑耶。然则其心亦可谓戚矣。未知正平之意其果然乎。 崇祯横艾困敦季夏十二日。华阳老叟书。洪州鲁恩洞迁奉成先生神主记
今 上壬子四月日。京中儒士南宅夏,张始显,吕必宽三人以书来曰。某月日。户曹书吏严义龙来告成某神主在仁王山崩崖间。生等惊且异。奔往视之。崩崖乱石间有瓷器。其中有三个栗主。其一果成先生也。拂拭埃藓而审之。外面直书姓名三字及年戊戌生四字。陷中如之。而只少生之一字。合内外十三字矣。生等心神悚然。遂展拜以致礼焉。其二即先生外孙参赞朴壕夫妇也。其所题则一如家礼之式矣。生等不知如何处之。还以安置于旧处。未知将何以处之而得其宜也。余不觉怆叹曰。今去 世祖丙子。盖数百年矣。虽其显扬于当时者。无不声沈响灭。其鬼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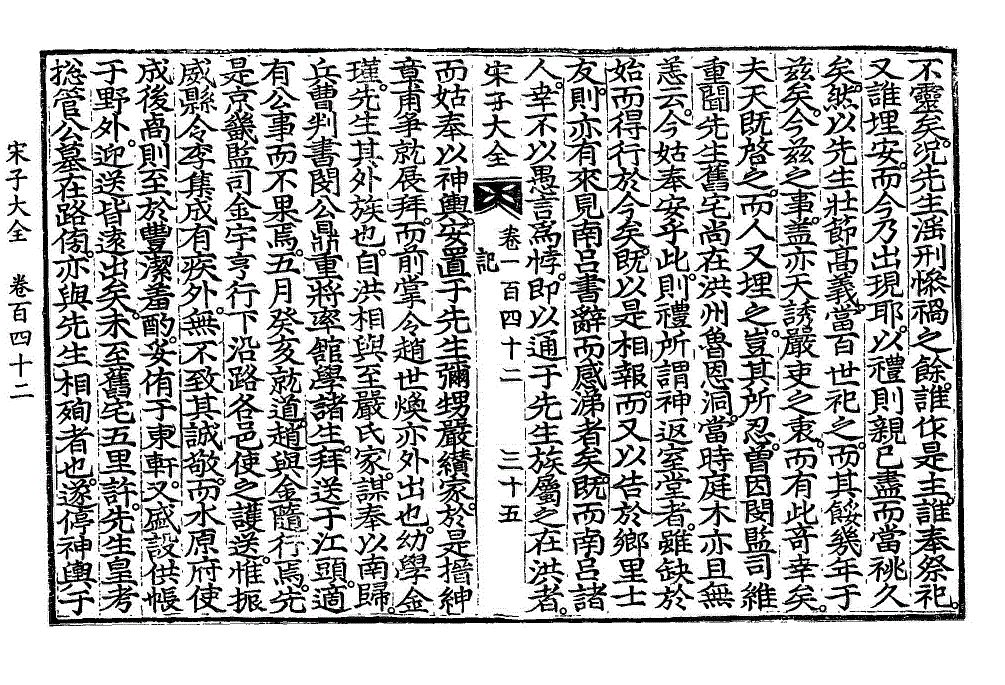 不灵矣。况先生淫刑惨祸之馀。谁作是主。谁奉祭祀。又谁埋安。而今乃出现耶。以礼则亲已尽而当祧久矣。然以先生壮节高义。当百世祀之。而其馁几年于兹矣。今兹之事。盖亦天诱严吏之衷。而有此奇幸矣。夫天既启之。而人又埋之。岂其所忍。曾因闵监司维重闻先生旧宅尚在洪州鲁恩洞。当时庭木亦且无恙云。今姑奉安乎此。则礼所谓神返室堂者。虽缺于始而得行于今矣。既以是相报。而又以告于乡里士友。则亦有来见南,吕书辞而感涕者矣。既而南,吕诸人。幸不以愚言为悖。即以通于先生族属之在洪者。而姑奉以神舆。安置于先生弥甥严缵家。于是搢绅章甫争就展拜。而前掌令赵世焕亦外出也。幼学金瑾。先生其外族也。自洪相与至严氏家。谋奉以南归。兵曹判书闵公鼎重将率馆学诸生。拜送于江头。适有公事而不果焉。五月癸亥就道。赵与金随行焉。先是京畿监司金宇亨行下沿路各邑使之护送。惟振威县令李集成有疾外。无不致其诚敬。而水原府使成后卨则至于丰洁羞酌。妥侑于东轩。又盛设供帐于野外。迎送皆远出矣。未至旧宅五里许。先生皇考总管公墓在路傍。亦与先生相殉者也。遂停神舆于
不灵矣。况先生淫刑惨祸之馀。谁作是主。谁奉祭祀。又谁埋安。而今乃出现耶。以礼则亲已尽而当祧久矣。然以先生壮节高义。当百世祀之。而其馁几年于兹矣。今兹之事。盖亦天诱严吏之衷。而有此奇幸矣。夫天既启之。而人又埋之。岂其所忍。曾因闵监司维重闻先生旧宅尚在洪州鲁恩洞。当时庭木亦且无恙云。今姑奉安乎此。则礼所谓神返室堂者。虽缺于始而得行于今矣。既以是相报。而又以告于乡里士友。则亦有来见南,吕书辞而感涕者矣。既而南,吕诸人。幸不以愚言为悖。即以通于先生族属之在洪者。而姑奉以神舆。安置于先生弥甥严缵家。于是搢绅章甫争就展拜。而前掌令赵世焕亦外出也。幼学金瑾。先生其外族也。自洪相与至严氏家。谋奉以南归。兵曹判书闵公鼎重将率馆学诸生。拜送于江头。适有公事而不果焉。五月癸亥就道。赵与金随行焉。先是京畿监司金宇亨行下沿路各邑使之护送。惟振威县令李集成有疾外。无不致其诚敬。而水原府使成后卨则至于丰洁羞酌。妥侑于东轩。又盛设供帐于野外。迎送皆远出矣。未至旧宅五里许。先生皇考总管公墓在路傍。亦与先生相殉者也。遂停神舆于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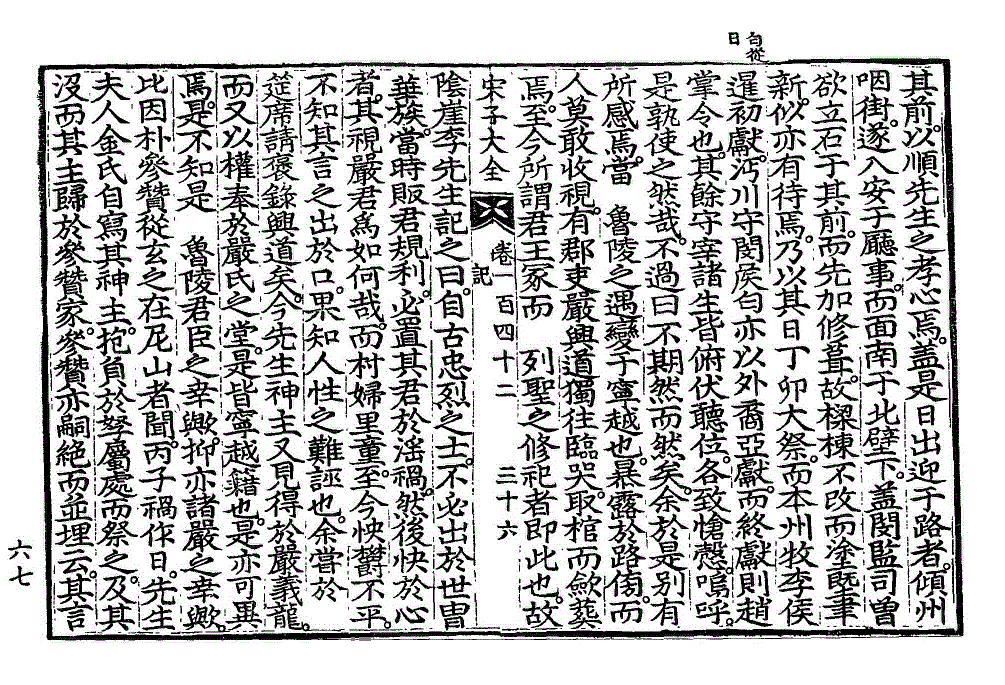 其前。以顺先生之孝心焉。盖是日出迎于路者。倾州咽街。遂入安于厅事。而面南于北壁下。盖闵监司曾欲立石于其前。而先加修葺。故梁栋不改而涂塈聿新。似亦有待焉。乃以其日丁卯大祭。而本州牧李侯暹初献。沔川守闵侯白(白从日)亦以外裔亚献。而终献则赵掌令也。其馀守宰诸生皆俯伏听位。各致怆悫。呜呼。是孰使之然哉。不过曰不期然而然矣。余于是别有所感焉。当 鲁陵之遇变于宁越也。暴露于路傍。而人莫敢收视。有郡吏严兴道独往临哭。取棺而敛葬焉。至今所谓君王冢而 列圣之修祀者即此也。故阴崖李先生记之曰。自古忠烈之士。不必出于世胄华族。当时贩君规利。必置其君于淫祸。然后快于心者。其视严君为如何哉。而村妇里童。至今怏郁不平。不知其言之出于口。果知人性之难诬也。余尝于 筵席请褒录兴道矣。今先生神主又见得于严义龙。而又以权奉于严氏之堂。是皆宁越籍也。是亦可异焉。是不知是 鲁陵君臣之幸欤。抑亦诸严之幸欤。比因朴参赞从玄之在尼山者闻。丙子祸作日。先生夫人金氏自写其神主。抱负于孥属处而祭之。及其没而其主归于参赞家。参赞亦嗣绝而并埋云。其言
其前。以顺先生之孝心焉。盖是日出迎于路者。倾州咽街。遂入安于厅事。而面南于北壁下。盖闵监司曾欲立石于其前。而先加修葺。故梁栋不改而涂塈聿新。似亦有待焉。乃以其日丁卯大祭。而本州牧李侯暹初献。沔川守闵侯白(白从日)亦以外裔亚献。而终献则赵掌令也。其馀守宰诸生皆俯伏听位。各致怆悫。呜呼。是孰使之然哉。不过曰不期然而然矣。余于是别有所感焉。当 鲁陵之遇变于宁越也。暴露于路傍。而人莫敢收视。有郡吏严兴道独往临哭。取棺而敛葬焉。至今所谓君王冢而 列圣之修祀者即此也。故阴崖李先生记之曰。自古忠烈之士。不必出于世胄华族。当时贩君规利。必置其君于淫祸。然后快于心者。其视严君为如何哉。而村妇里童。至今怏郁不平。不知其言之出于口。果知人性之难诬也。余尝于 筵席请褒录兴道矣。今先生神主又见得于严义龙。而又以权奉于严氏之堂。是皆宁越籍也。是亦可异焉。是不知是 鲁陵君臣之幸欤。抑亦诸严之幸欤。比因朴参赞从玄之在尼山者闻。丙子祸作日。先生夫人金氏自写其神主。抱负于孥属处而祭之。及其没而其主归于参赞家。参赞亦嗣绝而并埋云。其言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8H 页
 皆可徵矣。其夫人墓今在鲁恩洞。香火废绝。呜呼。其亦悲矣。京外诸生又将作庙于宅傍。并享当时同志朴河李柳俞五先生。盖以为 世祖大王尝有成某等万世忠臣之教。故河先生之祠建于善山。朴先生之碑立于怀德。而朝廷无禁焉矣。闵监司所伐之石。已致于宅前。而未及磨刻。今祠与石二役。州牧李侯及沔川闵守将终始经纪云。是岁七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皆可徵矣。其夫人墓今在鲁恩洞。香火废绝。呜呼。其亦悲矣。京外诸生又将作庙于宅傍。并享当时同志朴河李柳俞五先生。盖以为 世祖大王尝有成某等万世忠臣之教。故河先生之祠建于善山。朴先生之碑立于怀德。而朝廷无禁焉矣。闵监司所伐之石。已致于宅前。而未及磨刻。今祠与石二役。州牧李侯及沔川闵守将终始经纪云。是岁七月日。恩津宋时烈记。不知村记
表侄金生得洙卜筑于三山之治东五里而近。一日吾友月城金重举过其村。因其旧名之俚而名以不知。曩清阴金先生改贼室为石室。溪山草木。亦皆光荣。今是村亦不可谓不遇矣。既金生请问重举名之之意。余曰厚哉。重举之意也。是以天谓文王之意而望汝也。其意若曰颜渊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亦将以文何人余何人。期勉焉尔。夫所谓不知者。不作自己聪明。一循乎天理之谓(谓一作正)也。圣贤学问之道。岂有以加于此哉。然此是圣人事。难遽凑泊矣。若然则将负重举之意乎。曰登高行远者。必自卑近。愚将以卑近者告汝乎。汝虽贱微。而不知人爵位之可贵。汝虽贫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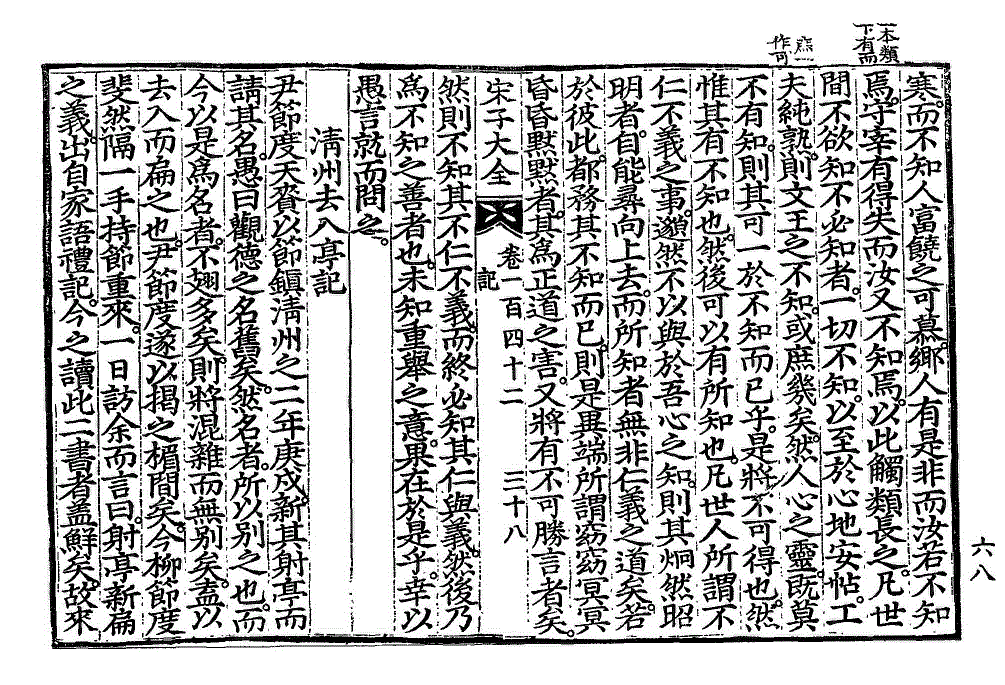 寒。而不知人富饶之可慕。乡人有是非而汝若不知焉。守宰有得失而汝又不知焉。以此触类(一本类下有而)长之。凡世间不欲知不必知者。一切不知。以至于心地安帖。工夫纯熟。则文王之不知。或庶(庶一作可)几矣。然人心之灵。既莫不有知。则其可一于不知而已乎。是将不可得也。然惟其有不知也。然后可以有所知也。凡世人所谓不仁不义之事。邈然不以与于吾心之知。则其炯然昭明者。自能寻向上去。而所知者无非仁义之道矣。若于彼此。都务其不知而已。则是异端所谓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者。其为正道之害。又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然则不知其不仁不义。而终必知其仁与义。然后乃为不知之善者也。未知重举之意。果在于是乎。幸以愚言就而问之。
寒。而不知人富饶之可慕。乡人有是非而汝若不知焉。守宰有得失而汝又不知焉。以此触类(一本类下有而)长之。凡世间不欲知不必知者。一切不知。以至于心地安帖。工夫纯熟。则文王之不知。或庶(庶一作可)几矣。然人心之灵。既莫不有知。则其可一于不知而已乎。是将不可得也。然惟其有不知也。然后可以有所知也。凡世人所谓不仁不义之事。邈然不以与于吾心之知。则其炯然昭明者。自能寻向上去。而所知者无非仁义之道矣。若于彼此。都务其不知而已。则是异端所谓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者。其为正道之害。又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然则不知其不仁不义。而终必知其仁与义。然后乃为不知之善者也。未知重举之意。果在于是乎。幸以愚言就而问之。清州去入亭记
尹节度天赉以节镇清州之二年庚戌。新其射亭而请其名。愚曰观德之名旧矣。然名者。所以别之也。而今以是为名者。不翅多矣。则将混杂而无别矣。盍以去入而扁之也。尹节度遂以揭之楣间矣。今柳节度斐然隔一手持节重来。一日访余而言曰。射亭新扁之义。出自家语礼记。今之读此二书者盖鲜矣。故来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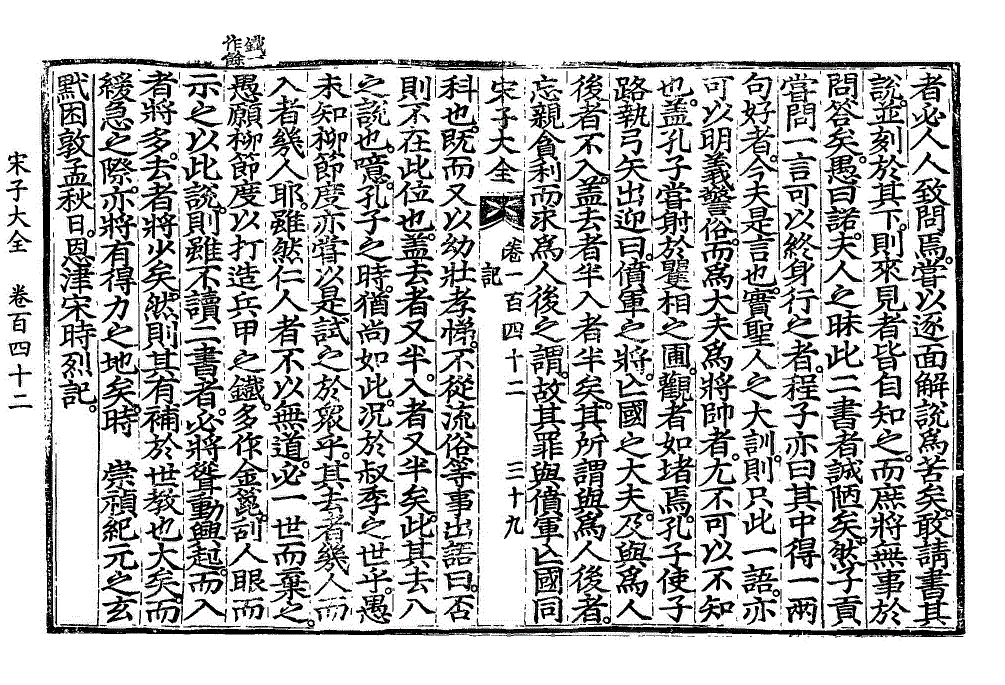 者必人人致问焉。尝以逐面解说为苦矣。敢请书其说。并刻于其下。则来见者皆自知之。而庶将无事于问答矣。愚曰诺。夫人之昧此二书者诚陋矣。然子贡尝问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程子亦曰其中得一两句好者。今夫是言也。实圣人之大训。则只此一语。亦可以明义警俗。而为大夫为将帅者。尤不可以不知也。盖孔子尝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焉。孔子使子路执弓矢出迎曰。偾军之将。亡国之大夫。及与为人后者不入。盖去者半入者半矣。其所谓与为人后者。忘亲贪利而求为人后之谓。故其罪与偾军亡国同科也。既而又以幼壮孝悌。不从流俗等事出语曰。否则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又半。入者又半矣。此其去入之说也。噫。孔子之时。犹尚如此。况于叔季之世乎。愚未知柳节度亦尝以是试之于众乎。其去者几人而入者几人耶。虽然仁人者不以无道。必一世而弃之。愚愿柳节度以打造兵甲之铁(铁一作馀)。多作金篦。刮人眼而示之以此说。则虽不读二书者。必将耸动兴起。而入者将多。去者将少矣。然则其有补于世教也大矣。而缓急之际。亦将有得力之地矣。时 崇祯纪元之玄黓困敦孟秋日。恩津宋时烈记。
者必人人致问焉。尝以逐面解说为苦矣。敢请书其说。并刻于其下。则来见者皆自知之。而庶将无事于问答矣。愚曰诺。夫人之昧此二书者诚陋矣。然子贡尝问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程子亦曰其中得一两句好者。今夫是言也。实圣人之大训。则只此一语。亦可以明义警俗。而为大夫为将帅者。尤不可以不知也。盖孔子尝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焉。孔子使子路执弓矢出迎曰。偾军之将。亡国之大夫。及与为人后者不入。盖去者半入者半矣。其所谓与为人后者。忘亲贪利而求为人后之谓。故其罪与偾军亡国同科也。既而又以幼壮孝悌。不从流俗等事出语曰。否则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又半。入者又半矣。此其去入之说也。噫。孔子之时。犹尚如此。况于叔季之世乎。愚未知柳节度亦尝以是试之于众乎。其去者几人而入者几人耶。虽然仁人者不以无道。必一世而弃之。愚愿柳节度以打造兵甲之铁(铁一作馀)。多作金篦。刮人眼而示之以此说。则虽不读二书者。必将耸动兴起。而入者将多。去者将少矣。然则其有补于世教也大矣。而缓急之际。亦将有得力之地矣。时 崇祯纪元之玄黓困敦孟秋日。恩津宋时烈记。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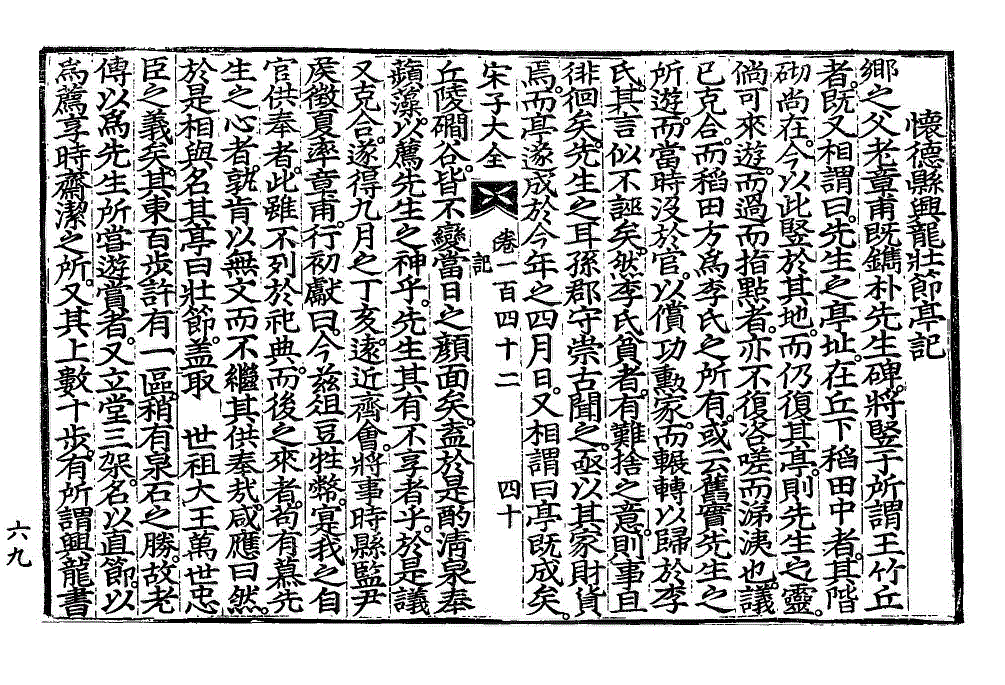 怀德县兴龙壮节亭记
怀德县兴龙壮节亭记乡之父老章甫既镌朴先生碑。将竖于所谓王竹丘者。既又相谓曰。先生之亭址。在丘下稻田中者。其阶砌尚在。今以此竖于其地。而仍复其亭。则先生之灵。倘可来游。而过而指点者。亦不复咨嗟而涕洟也。议已克合。而稻田方为李氏之所有。或云旧实先生之所游。而当时没于官。以偿功勋家。而辗转以归于李氏。其言似不诬矣。然李氏贫者。有难舍之意。则事且徘徊矣。先生之耳孙郡守崇古闻之。亟以其家财货焉。而亭遂成于今年之四月日。又相谓曰亭既成矣。丘陵涧谷。皆不变当日之颜面矣。盍于是酌清泉奉蘋藻。以荐先生之神乎。先生其有不享者乎。于是议又克合。遂得九月之丁亥。远近齐会。将事时县监尹侯徵夏率章甫。行初献曰。今兹俎豆牲币。寔我之自官供奉者。此虽不列于祀典。而后之来者。苟有慕先生之心者。孰肯以无文而不继其供奉哉。咸应曰然。于是相与名其亭曰壮节。盖取 世祖大王万世忠臣之义矣。其东百步许有一区。稍有泉石之胜。故老传以为先生所尝游赏者。又立堂三架。名以直节。以为荐享时斋洁之所。又其上数十步。有所谓兴龙书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0H 页
 堂者。是则邑中后生曾所建立。以为藏修之所者也。尹侯又定閒丁几人。以为典守碑亭之役云。
堂者。是则邑中后生曾所建立。以为藏修之所者也。尹侯又定閒丁几人。以为典守碑亭之役云。祥云驿和风馆记
祥云驿旧在襄阳府治之南二十里许。谚传以为尝有五彩云凝聚其地。因以为名。而其丞所居之馆。亦以是名焉。既而以风气之恶。人甚病焉。更于府内卜地置馆。而仍揭以祥云之名矣。今 上十二年。儿子基泰为丞兹驿。嫌其名之爽实。尝归省而告曰。愿有以改之。余曰祥云之名甚佳。舍之可惜。然朱夫子尝以和风云者。媲之祥云。以赞程明道之德。今若以此而易彼。则是犹凤去而麟至矣。况岭东之地。大抵多风。而襄为最甚。今此馆之所处。独免其拔屋飘瓦。则今所改新名。真得其实矣。然驿隶之所以为患者。实在于为丞者之饕虐。而风之为患次之。苟使为丞者。横目自营。而无仁恕之心以加焉。则虽使和风日吹。草木冬荣。亦何以解其愠哉。凡为丞于此地者。顾名而思义则其庶矣乎。呜呼。明道之有此祥和之气者。岂徒然哉。盖尝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又曰常愧视民如伤四字。其仁爱之心如此。故其符见于外者。不期然而然矣。凡为丞于此者。不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0L 页
 徒慕其名而思效其实之万一。则虽使恶风翻海而至。还如庇之以大厦。被之以温纩矣。儿子莅任已经年岁矣。未知丞负汝乎。汝负丞乎。苟不以明道之心为心。则其不但负丞。而负此新揭之名也大矣。可不惧哉。遂书此以畀之。并以谂于后人云。 崇祯壬子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徒慕其名而思效其实之万一。则虽使恶风翻海而至。还如庇之以大厦。被之以温纩矣。儿子莅任已经年岁矣。未知丞负汝乎。汝负丞乎。苟不以明道之心为心。则其不但负丞。而负此新揭之名也大矣。可不惧哉。遂书此以畀之。并以谂于后人云。 崇祯壬子月日。恩津宋时烈记。东郭新居后记
余窃见金公起之所记东郭新居。不能无所疑于心者。其曰幼学壮行。致君尧舜者。自士君子之至愿。而乃以七尺之躯。汩没于宦海澜翻之中。不能自拔于钟鸣漏尽之后者多矣。此岂公以壮行之年。而将欲告老之意也欤。第公位至卿月。 圣上倚任。其所以行其所学。有何不可。而犹不愿于士君子所愿者。岂犹有所不乐于心者哉。是未可知也。及读其篇末也。乃释然于心而恍然而叹也。其曰吾先祖考难进易退之节。终始不苟。归卧石室者过半。所谓石室者。非有江湖泉石之乐。则必有其可乐之实。而非他人所可知也。呜呼。文正先生之乐。果非他人之所敢知。而公则知之。故将以其所乐为乐。而有继述之志也。然君子之所谓乐。岂易言哉。陋巷箪瓢之乐。濂溪不以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1H 页
 告于二程。程先生亦引而不发。邵先生亦自言其真乐攻心。而终不言其所乐者何事。夫君子之乐。得之于心。其胸次自不觉其悠然。而天下万物皆无以易焉。则诚非外人之所可知。而惟公则自为赤子时。提挈于左右。而又有所闻于趋庭之日。耳擩目染。无非所乐之实。则无惑乎他人不知而公独知之也。呜呼。文正先生之所乐。即颜邵之所乐。则真可谓大且深矣。惟朱夫子所言。其于今日事。尤有至切而至要者。今请为公而诵之也。夫子之言曰。幼而学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怵迫势利。眷眷轩冕而不能归。或归矣而酣豢之馀。厌苦淡泊。顾慕畴昔。咨嗟戚促。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顾其前日从宦之所为。不能无愧悔于心者。则其于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固不能也。然则仕而能归。归而能乐。岂不难哉。至哉言乎。今公之志如此。则其能归也必矣。而其未归之前。将无愧悔。是图是度。则其归而能乐也。可保无疑矣。文正先生之所乐。亦无乃由此而得之耶。敢以为问而因以勉焉。时 崇祯壬子长至后日。恩津宋时烈记。
告于二程。程先生亦引而不发。邵先生亦自言其真乐攻心。而终不言其所乐者何事。夫君子之乐。得之于心。其胸次自不觉其悠然。而天下万物皆无以易焉。则诚非外人之所可知。而惟公则自为赤子时。提挈于左右。而又有所闻于趋庭之日。耳擩目染。无非所乐之实。则无惑乎他人不知而公独知之也。呜呼。文正先生之所乐。即颜邵之所乐。则真可谓大且深矣。惟朱夫子所言。其于今日事。尤有至切而至要者。今请为公而诵之也。夫子之言曰。幼而学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怵迫势利。眷眷轩冕而不能归。或归矣而酣豢之馀。厌苦淡泊。顾慕畴昔。咨嗟戚促。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顾其前日从宦之所为。不能无愧悔于心者。则其于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固不能也。然则仕而能归。归而能乐。岂不难哉。至哉言乎。今公之志如此。则其能归也必矣。而其未归之前。将无愧悔。是图是度。则其归而能乐也。可保无疑矣。文正先生之所乐。亦无乃由此而得之耶。敢以为问而因以勉焉。时 崇祯壬子长至后日。恩津宋时烈记。怀德县新洞社仓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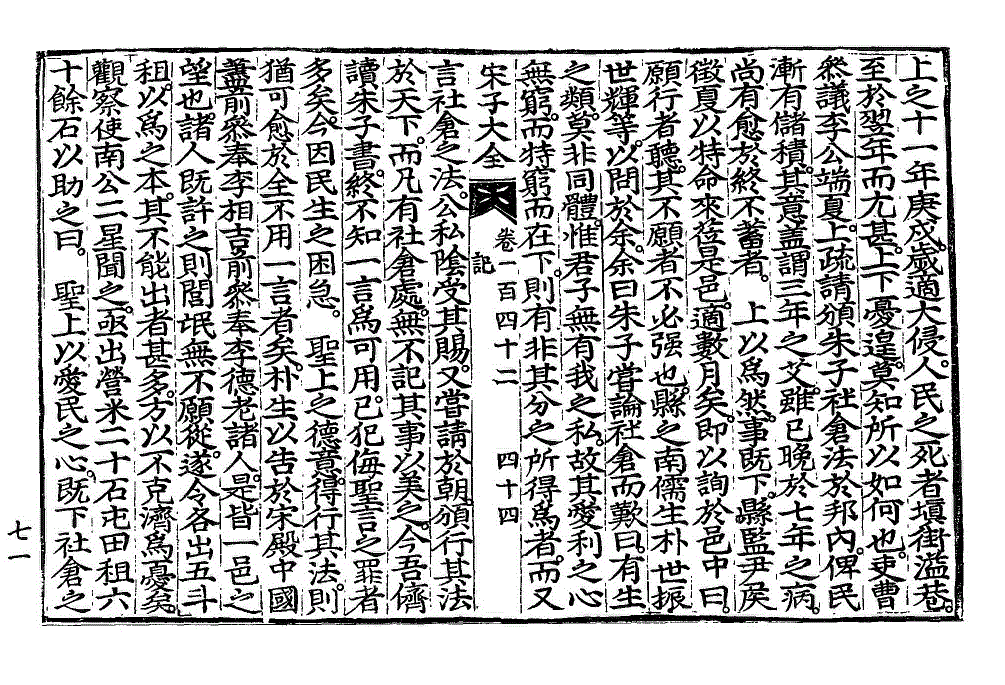 上之十一年庚戌。岁适大侵。人民之死者填街溢巷。至于翌年而尤甚。上下忧遑。莫知所以如何也。吏曹参议李公端夏。上疏请颁朱子社仓法于邦内。俾民渐有储积。其意盖谓三年之艾。虽已晚于七年之病。尚有愈于终不蓄者。 上以为然。事既下。县监尹侯徵夏以特命来莅是邑。适数月矣。即以询于邑中曰。愿行者听。其不愿者不必强也。县之南儒生朴世振,世辉等。以问于余。余曰朱子尝论社仓而叹曰。有生之类。莫非同体。惟君子无有我之私。故其爱利之心无穷。而特穷而在下。则有非其分之所得为者。而又言社仓之法。公私阴受其赐。又尝请于朝。颁行其法于天下。而凡有社仓处。无不记其事以美之。今吾侪读朱子书。终不知一言为可用。已犯侮圣言之罪者多矣。今因民生之困急。 圣上之德意。得行其法。则犹可愈于全不用一言者矣。朴生以告于宋殿中国荩前参奉李相吉,前参奉李德老诸人。是皆一邑之望也。诸人既许之则闾氓无不愿从。遂令各出五斗租。以为之本。其不能出者甚多。方以不克济为忧矣。观察使南公二星闻之。亟出营米二十石屯田租六十馀石以助之曰。 圣上以爱民之心。既下社仓之
上之十一年庚戌。岁适大侵。人民之死者填街溢巷。至于翌年而尤甚。上下忧遑。莫知所以如何也。吏曹参议李公端夏。上疏请颁朱子社仓法于邦内。俾民渐有储积。其意盖谓三年之艾。虽已晚于七年之病。尚有愈于终不蓄者。 上以为然。事既下。县监尹侯徵夏以特命来莅是邑。适数月矣。即以询于邑中曰。愿行者听。其不愿者不必强也。县之南儒生朴世振,世辉等。以问于余。余曰朱子尝论社仓而叹曰。有生之类。莫非同体。惟君子无有我之私。故其爱利之心无穷。而特穷而在下。则有非其分之所得为者。而又言社仓之法。公私阴受其赐。又尝请于朝。颁行其法于天下。而凡有社仓处。无不记其事以美之。今吾侪读朱子书。终不知一言为可用。已犯侮圣言之罪者多矣。今因民生之困急。 圣上之德意。得行其法。则犹可愈于全不用一言者矣。朴生以告于宋殿中国荩前参奉李相吉,前参奉李德老诸人。是皆一邑之望也。诸人既许之则闾氓无不愿从。遂令各出五斗租。以为之本。其不能出者甚多。方以不克济为忧矣。观察使南公二星闻之。亟出营米二十石屯田租六十馀石以助之曰。 圣上以爱民之心。既下社仓之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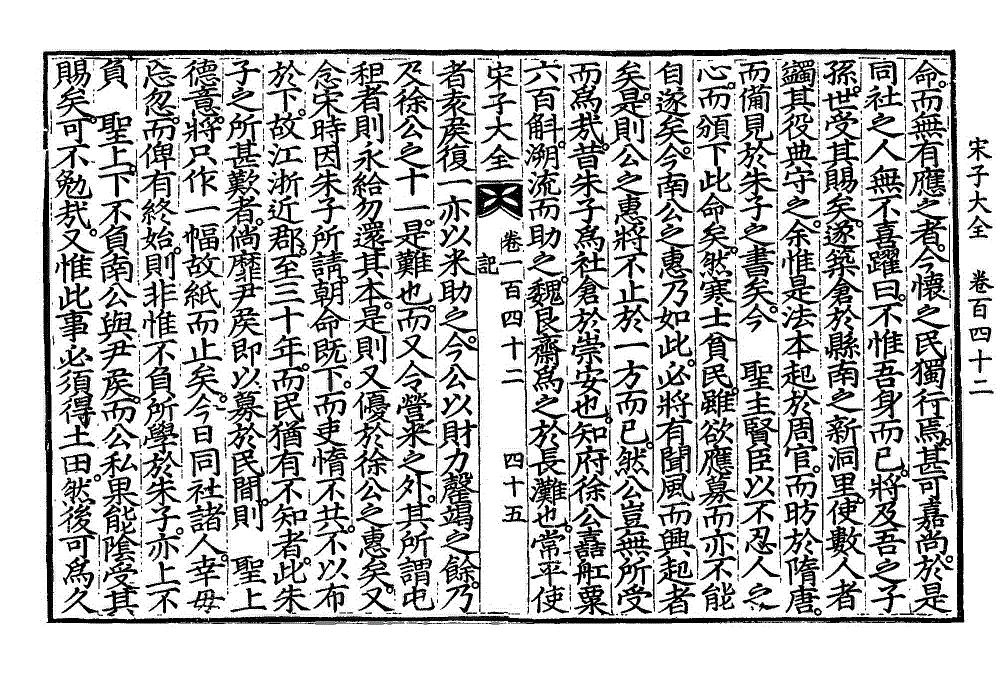 命。而无有应之者。今怀之民独行焉。甚可嘉尚。于是同社之人无不喜跃曰。不惟吾身而已。将及吾之子孙。世受其赐矣。遂筑仓于县南之新洞里。使数人者蠲其役典守之。余惟是法本起于周官。而昉于隋唐。而备见于朱子之书矣。今 圣主贤臣以不忍人之心。而颁下此命矣。然寒士贫民。虽欲应募而亦不能自遂矣。今南公之惠乃如此。必将有闻风而兴起者矣。是则公之惠将不止于一方而已。然公岂无所受而为哉。昔朱子为社仓于崇安也。知府徐公哲舡粟六百斛。溯流而助之。魏艮斋为之于长滩也。常平使者袁侯复一亦以米助之。今公以财力罄竭之馀。乃及徐公之十一。是难也。而又令营米之外。其所谓屯租者则永给勿还其本。是则又优于徐公之惠矣。又念宋时因朱子所请。朝命既下。而吏惰不共。不以布于下。故江浙近郡。至三十年。而民犹有不知者。此朱子之所甚叹者。倘靡尹侯即以募于民间。则 圣上德意。将只作一幅故纸而止矣。今日同社诸人。幸毋忘忽。而俾有终始。则非惟不负所学于朱子。亦上不负 圣上。下不负南公与尹侯。而公私果能阴受其赐矣。可不勉哉。又惟此事必须得土田。然后可为久
命。而无有应之者。今怀之民独行焉。甚可嘉尚。于是同社之人无不喜跃曰。不惟吾身而已。将及吾之子孙。世受其赐矣。遂筑仓于县南之新洞里。使数人者蠲其役典守之。余惟是法本起于周官。而昉于隋唐。而备见于朱子之书矣。今 圣主贤臣以不忍人之心。而颁下此命矣。然寒士贫民。虽欲应募而亦不能自遂矣。今南公之惠乃如此。必将有闻风而兴起者矣。是则公之惠将不止于一方而已。然公岂无所受而为哉。昔朱子为社仓于崇安也。知府徐公哲舡粟六百斛。溯流而助之。魏艮斋为之于长滩也。常平使者袁侯复一亦以米助之。今公以财力罄竭之馀。乃及徐公之十一。是难也。而又令营米之外。其所谓屯租者则永给勿还其本。是则又优于徐公之惠矣。又念宋时因朱子所请。朝命既下。而吏惰不共。不以布于下。故江浙近郡。至三十年。而民犹有不知者。此朱子之所甚叹者。倘靡尹侯即以募于民间。则 圣上德意。将只作一幅故纸而止矣。今日同社诸人。幸毋忘忽。而俾有终始。则非惟不负所学于朱子。亦上不负 圣上。下不负南公与尹侯。而公私果能阴受其赐矣。可不勉哉。又惟此事必须得土田。然后可为久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2L 页
 远之图。故宋之光泽县宰。以民田僧田之入官者。与之社仓。而朱子亦记之。今亦以此而告于观察公及县侯。似亦一事。未知如何。幸社中诸人相与议之。 崇祯壬子月日。
远之图。故宋之光泽县宰。以民田僧田之入官者。与之社仓。而朱子亦记之。今亦以此而告于观察公及县侯。似亦一事。未知如何。幸社中诸人相与议之。 崇祯壬子月日。易安室记
赵复亨结数椽于西郊之外先垄之下。以为栖息之所。而问名于余。余曰余方悯世人不揆其顶蹠。止于七尺之强弱。而务为高广之屋。以自侈大也。今兹数椽既成于不日。而又易安。古人有言鹤鹩易安于一枝。而晋陶靖节亦以容膝之衡宇为易安。今子之安于斯室也。亦甚易易矣。盍以是名之。复亨曰然。余又曰凡人有室。动作于事为。而入处则安。行役于道路。而泊定则安。此皆无待于外。不求于人。造次而得之者矣。斯不亦易易乎。然而仕宦之人。怵迫利害。眷顾冕绂。则不能归安于所安之处矣。其或归安。而厦毡之馀。厌苦卑隘。追慕畴昔。不能忘情。方且嗟呼悴郁。自以为不得其所。岂能知其为安耶。又其从前游宦之日。其所云为。有不能无悔怍于心者。则其羞愧熬于中。贬议交乎外矣。然则虽欲强而安之。其心固不能安也。心不安而身安者未之有也。然则虽曰易安。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3H 页
 而能安者实难矣。复亨尝读朱子书。既通籍入仕矣。若其论议行事。一用朱子之书。则将无所不安。而所难者实易矣。若或伛仰床席。抛弃经史。早眠晏起。无所猷为而曰。吾得所谓易安者。则非吾之所望也。
而能安者实难矣。复亨尝读朱子书。既通籍入仕矣。若其论议行事。一用朱子之书。则将无所不安。而所难者实易矣。若或伛仰床席。抛弃经史。早眠晏起。无所猷为而曰。吾得所谓易安者。则非吾之所望也。清州牧使南公遗爱阁记
上之十一年庚戌。以前大司谏南公九万为本州牧使。盖 上意以怀保小民为急也。岁适大侵。道殣狼籍(一作藉)。公不暇寝食。夙宵焦劳。凡所以救活沟壑。无所不用其极。而人死则曰是我罪也。死而不掩则又曰是我罪也。盖人皆罪岁。而公则罪己。其仁爱恻怛之诚。遍布旁达。浃于人之心肝。故其不幸而死者则曰。是我之无福。非公之不我尽也。于是流丐四集。填满街衢。公又一视同仁。恐有一毫彼此之间。故邻邑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焉。公又沥血陈疏。请蠲诸般逋负。又请截留田税之当输于京者。以为赈救之资。 上下其事。盖欲悉从其言。俾无靡孑之患。而庙堂乃以国计之哀痛。不能尽副所请。然其及民者亦不赀。而他邑因亦均被 圣上之德意。令既下。滨死之民皆欢欣鼓舞。虽深山穷谷。无不削木颂德。至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我公。或祝而书之曰。南公大夫人享寿无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3L 页
 疆。公谦不敢当。一皆踣之。而至于旁邑之民莫不皆然。则公亦不能禁也。当是时也。诸邑(邑一作道)之民。或欲上章于朝。乞以为监司者。或曰此唐藩镇逐帅自置之渐。不可为也。其事遂止。而朝廷竟移公使按咸镜道。北人之喜气。弸塞关岭。而州民如失慈母。皆赍咨涕洟。扳辕不忍舍。而 朝命催迫。公遂去矣。思欲立碑道逵。以不忘于永世。而顾以禁令之严而不敢焉。则遂立屋揭刻于楣间。以图不朽。或者曰公之德固深矣。然使公不遇大侵而施其喣濡。民亦感公如此之深乎。曰公之仁心。特因荒政而见其一端耳。既有是心则其随处感发者。何往而非仁哉。汉之宣光之世。未闻有饥歉。而犹乃有召父杜母之谣者是何也。夫公恻怛慈爱之心。未尝蔽于物欲。故其不忍人之政。如是其深切。而人顾乃以遇人之艰难。为公之幸。则是以褰裳濡足而救孺子之入井者。谓无是心于平常无事之时也。其可乎哉。东莱先生曰云霓之望。非汤之幸。乃汤之不幸。仁人之心。岂幸于民穷。而悦我之惠乎。其心苟或一毫如是。则虽日活万人。其至愚而神者。必如蒙袂辑屦者之不食而宁死矣。此诚伪之分也。然鲁君不掣子贱之肘。然后能成单父之治。距
疆。公谦不敢当。一皆踣之。而至于旁邑之民莫不皆然。则公亦不能禁也。当是时也。诸邑(邑一作道)之民。或欲上章于朝。乞以为监司者。或曰此唐藩镇逐帅自置之渐。不可为也。其事遂止。而朝廷竟移公使按咸镜道。北人之喜气。弸塞关岭。而州民如失慈母。皆赍咨涕洟。扳辕不忍舍。而 朝命催迫。公遂去矣。思欲立碑道逵。以不忘于永世。而顾以禁令之严而不敢焉。则遂立屋揭刻于楣间。以图不朽。或者曰公之德固深矣。然使公不遇大侵而施其喣濡。民亦感公如此之深乎。曰公之仁心。特因荒政而见其一端耳。既有是心则其随处感发者。何往而非仁哉。汉之宣光之世。未闻有饥歉。而犹乃有召父杜母之谣者是何也。夫公恻怛慈爱之心。未尝蔽于物欲。故其不忍人之政。如是其深切。而人顾乃以遇人之艰难。为公之幸。则是以褰裳濡足而救孺子之入井者。谓无是心于平常无事之时也。其可乎哉。东莱先生曰云霓之望。非汤之幸。乃汤之不幸。仁人之心。岂幸于民穷。而悦我之惠乎。其心苟或一毫如是。则虽日活万人。其至愚而神者。必如蒙袂辑屦者之不食而宁死矣。此诚伪之分也。然鲁君不掣子贱之肘。然后能成单父之治。距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4H 页
 心不得刍牧之求。则立视牛羊之死。今公之心。虽至仁。而苟非 圣上特准其所请。则惠泽何以及于民哉。故民之归德于公者。公不自有而归之 圣上。亦可见为臣之恭矣。公既去而岁仍不登。民甚困厄。则论者益恨公疏之所请。不尽行于当日。而幸今本道观察公复上章申公之说。则 圣上多采施焉。观察公即公之叔父也。公之家法之善固如此。而窃恐蒙公之惠者。虽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如朱夫子所云。故并记之。 崇祯纪元之后四十五年横艾困敦季冬日。州民恩津宋时烈记。
心不得刍牧之求。则立视牛羊之死。今公之心。虽至仁。而苟非 圣上特准其所请。则惠泽何以及于民哉。故民之归德于公者。公不自有而归之 圣上。亦可见为臣之恭矣。公既去而岁仍不登。民甚困厄。则论者益恨公疏之所请。不尽行于当日。而幸今本道观察公复上章申公之说。则 圣上多采施焉。观察公即公之叔父也。公之家法之善固如此。而窃恐蒙公之惠者。虽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如朱夫子所云。故并记之。 崇祯纪元之后四十五年横艾困敦季冬日。州民恩津宋时烈记。集义斋记
程子称孟子有功于圣门者。是便说许多养气出来。然养气之本。又在集义。则圣学之要。岂有以易此哉。只是孟子始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而又须说是集义所生者何也。盖以天地言之则须先有理而后有气。故所谓阴阳者。始则生于太极。而及其造化发育之时。则又其所谓阴阳者。经纬错综而后。太极之理亦得而分俵万物。而万物各正性命。是则阴阳虽曰形于下者。而未尝不运用乎太极也。以其在人者言之。则道义是天地之理也。气是天地之阴阳也。故此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二 第 74L 页
 浩然之气。始虽生于道义。而既生之后则还以扶助道义也。然孟子后千有馀年。被人看不破说不行。故朱子发明其义。极其仔细。殆至万馀言而曰。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则天厌之。然则孟子固有功于圣门。而朱子之功实不在孟子之下矣。阳川许生瑗来处华阳山中。与余共读朱子书。一日谓余曰。生所居之室。尝因其地名名以集义。愿有说以明其义也。余既略举朱子语论说其梗槩。而因又告之曰。义不可以徒集。必先有以知之。而又当以敬为主。然后乃可以言集之之功。故朱子尝以格物致知。为明义之端。又尝曰不敬时便是不义。然则求集义而不先此二者。何异于适越而北辕哉。然此不待朱子说。而孟子已备言之。盖才说集义。而其下即承以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长。此虽集义节度。而敬便在其中矣。即又说知言之道。则知言便是格致之效(一本效下有也字归以恐归而)。愿生归以静处。以三夫子之说。对同勘合。则实千载而一符也。
浩然之气。始虽生于道义。而既生之后则还以扶助道义也。然孟子后千有馀年。被人看不破说不行。故朱子发明其义。极其仔细。殆至万馀言而曰。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则天厌之。然则孟子固有功于圣门。而朱子之功实不在孟子之下矣。阳川许生瑗来处华阳山中。与余共读朱子书。一日谓余曰。生所居之室。尝因其地名名以集义。愿有说以明其义也。余既略举朱子语论说其梗槩。而因又告之曰。义不可以徒集。必先有以知之。而又当以敬为主。然后乃可以言集之之功。故朱子尝以格物致知。为明义之端。又尝曰不敬时便是不义。然则求集义而不先此二者。何异于适越而北辕哉。然此不待朱子说。而孟子已备言之。盖才说集义。而其下即承以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长。此虽集义节度。而敬便在其中矣。即又说知言之道。则知言便是格致之效(一本效下有也字归以恐归而)。愿生归以静处。以三夫子之说。对同勘合。则实千载而一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