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x 页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记
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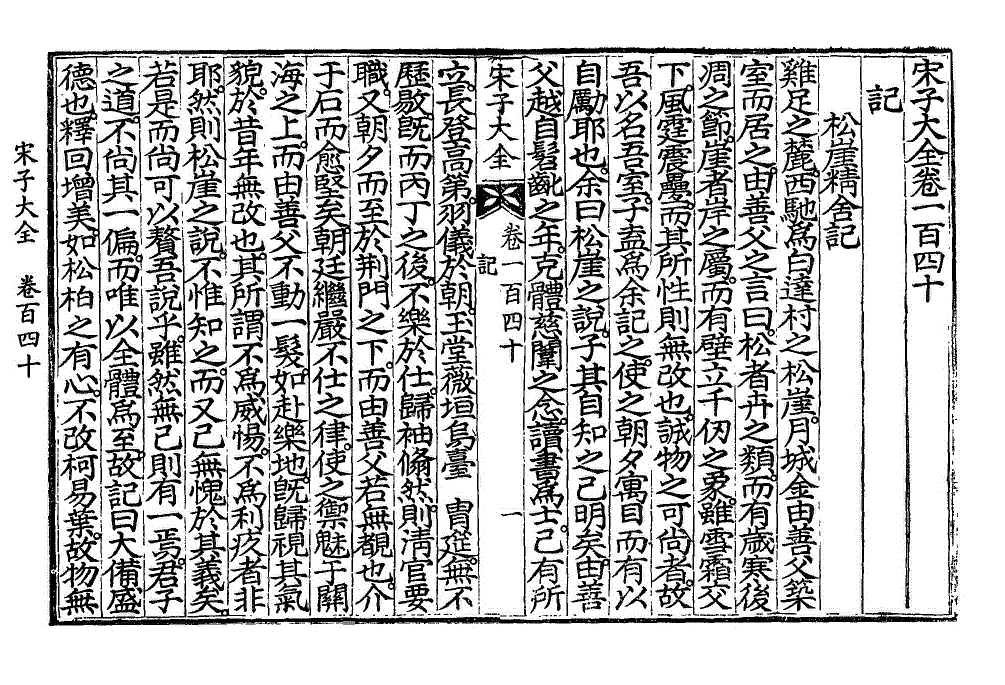 松崖精舍记
松崖精舍记鸡足之麓。西驰为白达村之松崖。月城金由善父筑室而居之。由善父之言曰。松者卉之类。而有岁寒后凋之节。崖者岸之属。而有壁立千仞之象。虽雪霜交下。风霆震叠。而其所性则无改也。诚物之可尚者。故吾以名吾室。子盍为余记之。使之朝夕寓目而有以自励耶也。余曰松崖之说。子其自知之已明矣。由善父越自髫龀之年。克体慈闱之念。读书为士。已有所立。长登高第。羽仪于朝。玉堂薇垣乌台 胄筵。无不历扬。既而丙丁之后。不乐于仕。归袖翛然。则清官要职。又朝夕而至于荆门之下。而由善父若无睹也。介于石而愈坚矣。朝廷继严不仕之律。使之御魅于关海之上。而由善父不动一发。如赴乐地。既归视其气貌。于昔年无改也。其所谓不为威惕。不为利疚者非耶。然则松崖之说。不惟知之。而又已无愧于其义矣。若是而尚可以赘吾说乎。虽然无已则有一焉。君子之道。不尚其一偏。而唯以全体为至。故记曰大备盛德也。释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易叶。故物无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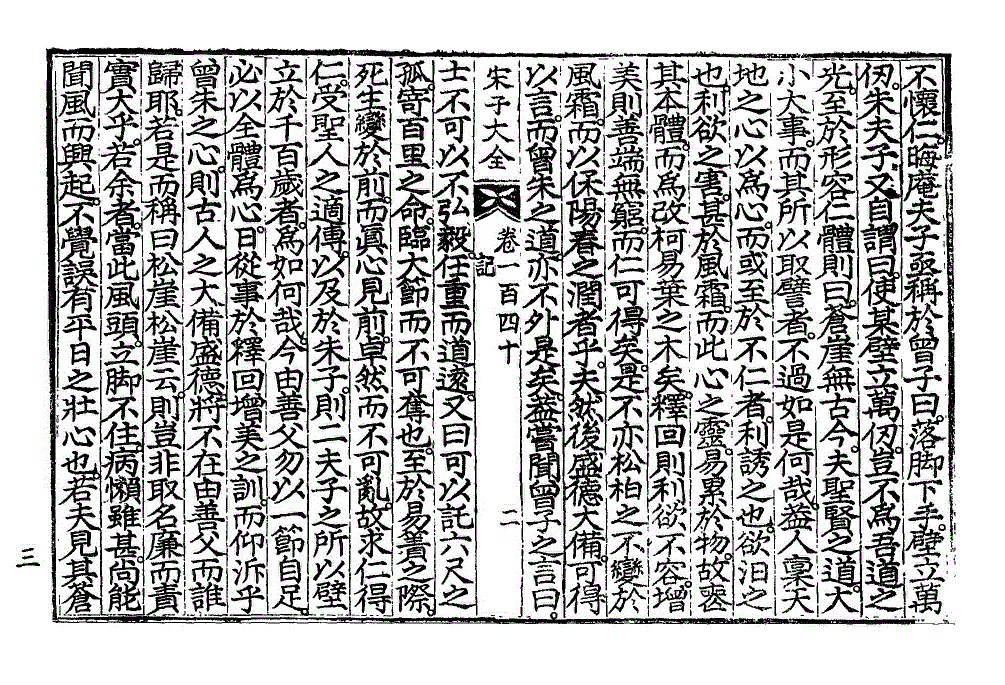 不怀仁。晦庵夫子亟称于曾子曰。落脚下手。壁立万仞。朱夫子又自谓曰。使某壁立万仞。岂不为吾道之光。至于形容仁体则曰。苍崖无古今。夫圣贤之道。大小大事。而其所以取譬者。不过如是何哉。盖人禀天地之心以为心。而或至于不仁者。利诱之也。欲汩之也。利欲之害。甚于风霜。而此心之灵。易累于物。故丧其本体。而为改柯易叶之木矣。释回则利欲不容。增美则善端无穷。而仁可得矣。是不亦松柏之不变于风霜。而以保阳春之润者乎。夫然后盛德大备。可得以言。而曾朱之道。亦不外是矣。盖尝闻曾子之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至于易箦之际。死生变于前。而真心见前。卓然而不可乱。故求仁得仁。受圣人之适传。以及于朱子。则二夫子之所以壁立于千百岁者。为如何哉。今由善父勿以一节自足。必以全体为心。日从事于释回增美之训。而仰溯乎曾朱之心。则古人之大备盛德。将不在由善父而谁归耶。若是而称曰松崖松崖云。则岂非取名廉而责实大乎。若余者。当此风头。立脚不住。病懒虽甚。尚能闻风而兴起。不觉误有平日之壮心也。若夫见其苍
不怀仁。晦庵夫子亟称于曾子曰。落脚下手。壁立万仞。朱夫子又自谓曰。使某壁立万仞。岂不为吾道之光。至于形容仁体则曰。苍崖无古今。夫圣贤之道。大小大事。而其所以取譬者。不过如是何哉。盖人禀天地之心以为心。而或至于不仁者。利诱之也。欲汩之也。利欲之害。甚于风霜。而此心之灵。易累于物。故丧其本体。而为改柯易叶之木矣。释回则利欲不容。增美则善端无穷。而仁可得矣。是不亦松柏之不变于风霜。而以保阳春之润者乎。夫然后盛德大备。可得以言。而曾朱之道。亦不外是矣。盖尝闻曾子之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至于易箦之际。死生变于前。而真心见前。卓然而不可乱。故求仁得仁。受圣人之适传。以及于朱子。则二夫子之所以壁立于千百岁者。为如何哉。今由善父勿以一节自足。必以全体为心。日从事于释回增美之训。而仰溯乎曾朱之心。则古人之大备盛德。将不在由善父而谁归耶。若是而称曰松崖松崖云。则岂非取名廉而责实大乎。若余者。当此风头。立脚不住。病懒虽甚。尚能闻风而兴起。不觉误有平日之壮心也。若夫见其苍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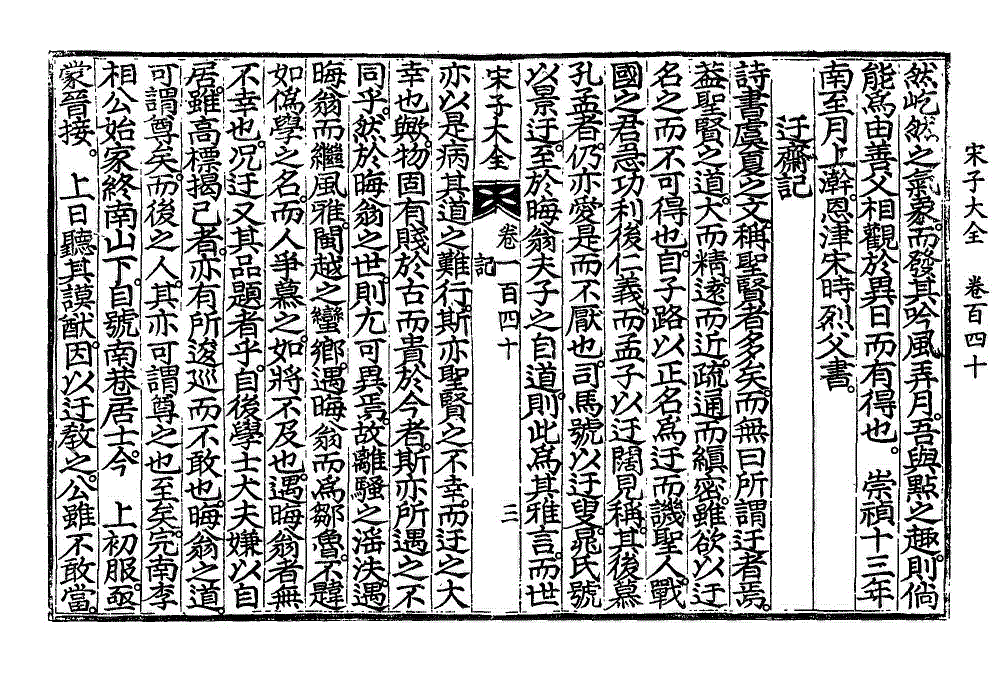 然屹然之气象。而发其吟风弄月。吾与点之趣。则倘能为由善父相观于异日而有得也。 崇祯十三年南至月上浣。恩津宋时烈父书。
然屹然之气象。而发其吟风弄月。吾与点之趣。则倘能为由善父相观于异日而有得也。 崇祯十三年南至月上浣。恩津宋时烈父书。迂斋记
诗书虞夏之文。称圣贤者多矣。而无曰所谓迂者焉。盖圣贤之道。大而精。远而近。疏通而缜密。虽欲以迂名之而不可得也。自子路以正名为迂而讥圣人。战国之君急功利后仁义。而孟子以迂阔见称。其后慕孔孟者。仍亦爱是而不厌也。司马号以迂叟。晁氏号以景迂。至于晦翁夫子之自道。则此为其雅言。而世亦以是病其道之难行。斯亦圣贤之不幸。而迂之大幸也欤。物固有贱于古而贵于今者。斯亦所遇之不同乎。然于晦翁之世。则尤可异焉。故离骚之淫泆。遇晦翁而继风雅。闽越之蛮乡。遇晦翁而为邹鲁。不韪如伪学之名。而人争慕之。如将不及也。遇晦翁者无不幸也。况迂又其品题者乎。自后学士大夫嫌以自居。虽高标揭己者。亦有所逡巡而不敢也。晦翁之道。可谓尊矣。而后之人。其亦可谓尊之也至矣。完南李相公始家终南山下。自号南巷居士。今 上初服。亟蒙晋接。 上日听其谟猷。因以迂教之。公虽不敢当。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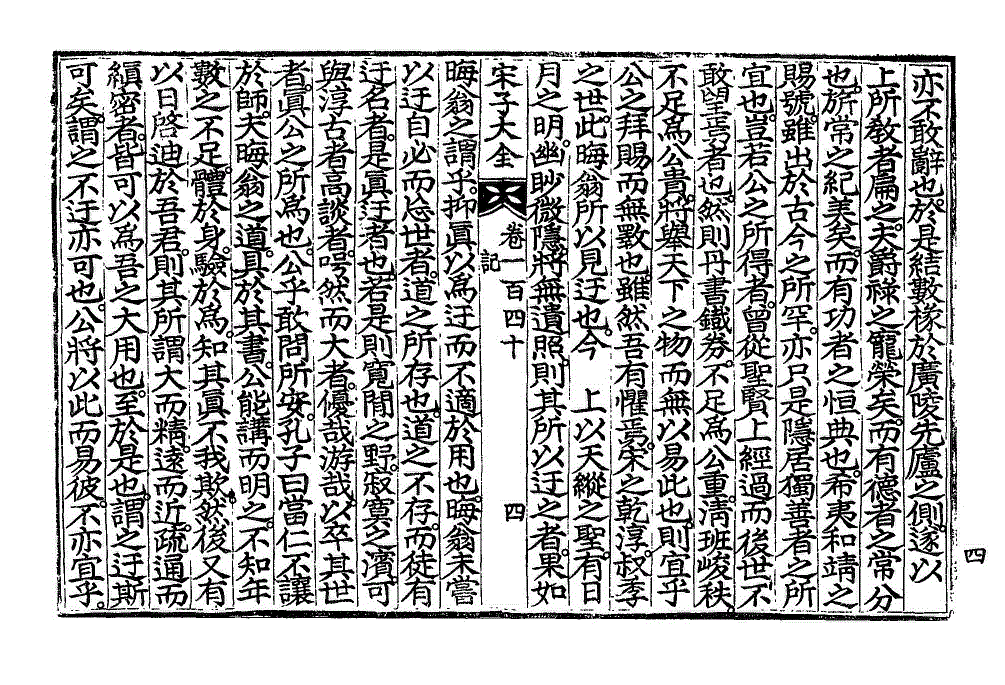 亦不敢辞也。于是结数椽于广陵先庐之侧。遂以 上所教者扁之。夫爵禄之宠荣矣。而有德者之常分也。旂常之纪美矣。而有功者之恒典也。希夷和靖之赐号。虽出于古今之所罕。亦只是隐居独善者之所宜也。岂若公之所得者。曾从圣贤上经过而后世不敢望焉者也。然则丹书铁券。不足为公重。清班峻秩。不足为公贵。将举天下之物而无以易此也。则宜乎公之拜赐而无斁也。虽然吾有惧焉。宋之乾淳。叔季之世。此晦翁所以见迂也。今 上以天纵之圣。有日月之明。幽眇微隐。将无遗照。则其所以迂之者。果如晦翁之谓乎。抑真以为迂而不适于用也。晦翁未尝以迂自必而忘世者。道之所存也。道之不存。而徒有迂名者。是真迂者也。若是则宽閒之野。寂寞之滨。可与淳古者高谈者。呺然而大者。优哉游哉。以卒其世者。真公之所为也。公乎敢问所安。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夫晦翁之道。具于其书。公能讲而明之。不知年数之不足。体于身。验于为。知其真不我欺。然后又有以日启迪于吾君。则其所谓大而精。远而近。疏通而缜密者。皆可以为吾之大用也。至于是也。谓之迂斯可矣。谓之不迂亦可也。公将以此而易彼。不亦宜乎。
亦不敢辞也。于是结数椽于广陵先庐之侧。遂以 上所教者扁之。夫爵禄之宠荣矣。而有德者之常分也。旂常之纪美矣。而有功者之恒典也。希夷和靖之赐号。虽出于古今之所罕。亦只是隐居独善者之所宜也。岂若公之所得者。曾从圣贤上经过而后世不敢望焉者也。然则丹书铁券。不足为公重。清班峻秩。不足为公贵。将举天下之物而无以易此也。则宜乎公之拜赐而无斁也。虽然吾有惧焉。宋之乾淳。叔季之世。此晦翁所以见迂也。今 上以天纵之圣。有日月之明。幽眇微隐。将无遗照。则其所以迂之者。果如晦翁之谓乎。抑真以为迂而不适于用也。晦翁未尝以迂自必而忘世者。道之所存也。道之不存。而徒有迂名者。是真迂者也。若是则宽閒之野。寂寞之滨。可与淳古者高谈者。呺然而大者。优哉游哉。以卒其世者。真公之所为也。公乎敢问所安。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夫晦翁之道。具于其书。公能讲而明之。不知年数之不足。体于身。验于为。知其真不我欺。然后又有以日启迪于吾君。则其所谓大而精。远而近。疏通而缜密者。皆可以为吾之大用也。至于是也。谓之迂斯可矣。谓之不迂亦可也。公将以此而易彼。不亦宜乎。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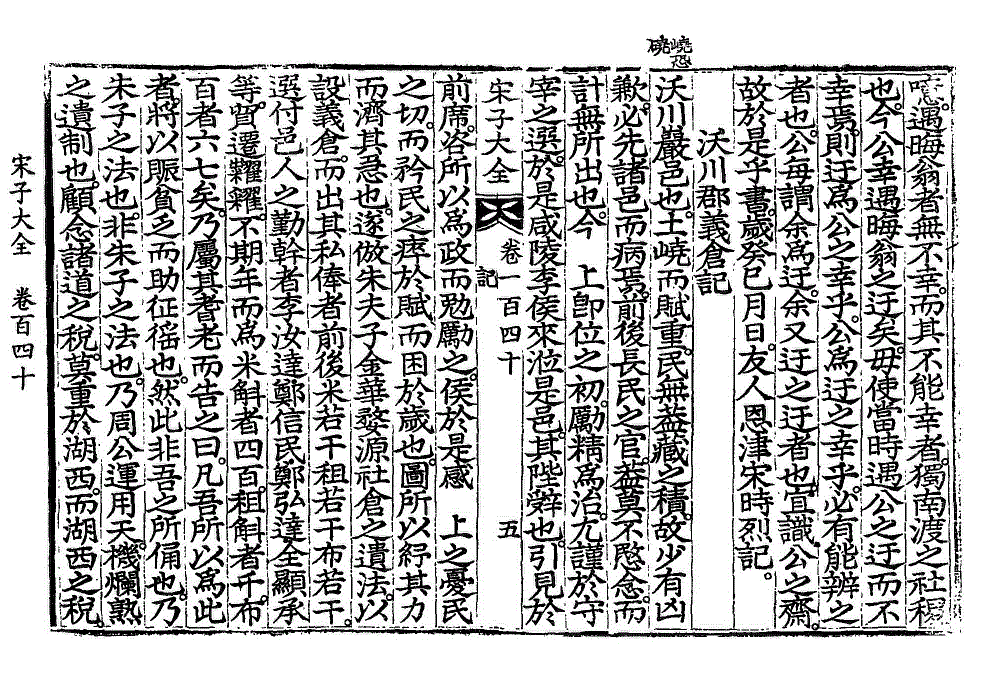 噫。遇晦翁者无不幸。而其不能幸者。独南渡之社稷也。今公幸遇晦翁之迂矣。毋使当时遇公之迂而不幸焉。则迂为公之幸乎。公为迂之幸乎。必有能辨之者也。公每谓余为迂。余又迂之迂者也。宜识公之斋。故于是乎书。岁癸巳月日。友人恩津宋时烈记。
噫。遇晦翁者无不幸。而其不能幸者。独南渡之社稷也。今公幸遇晦翁之迂矣。毋使当时遇公之迂而不幸焉。则迂为公之幸乎。公为迂之幸乎。必有能辨之者也。公每谓余为迂。余又迂之迂者也。宜识公之斋。故于是乎书。岁癸巳月日。友人恩津宋时烈记。沃川郡义仓记
沃川岩邑也。土峣(峣恐硗)而赋重。民无盖藏之积。故少有凶歉。必先诸邑而病焉。前后长民之官。盖莫不悯念。而计无所出也。今 上即位之初。励精为治。尤谨于守宰之选。于是咸陵李侯来涖是邑。其陛辞也。引见于前席。咨所以为政而勉励之。侯于是感 上之忧民之切。而矜民之瘁于赋而困于岁也。图所以纾其力而济其急也。遂仿朱夫子金华婺源社仓之遗法。以设义仓。而出其私俸者前后米若干租若干布若干。选付邑人之勤干者李汝达,郑信民,郑弘达,全显承等。贸迁粜籴。不期年而为米斛者四百。租斛者千。布百者六七矣。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凡吾所以为此者。将以赈贫乏而助征徭也。然此非吾之所俑也。乃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也。乃周公运用天机。烂熟之遗制也。顾念诸道之税。莫重于湖西。而湖西之税。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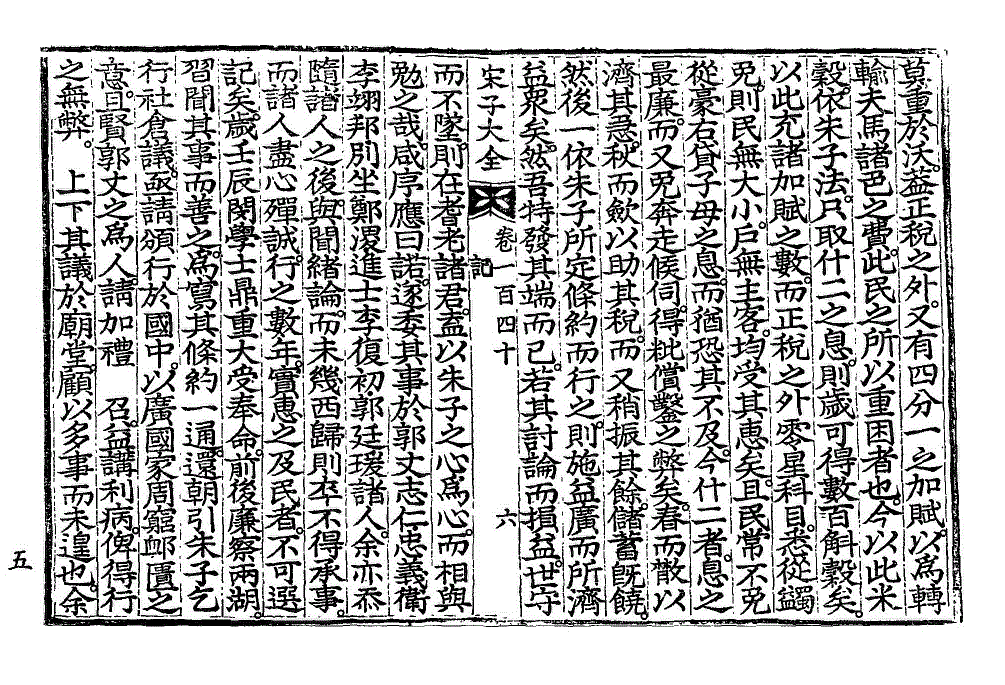 莫重于沃。盖正税之外。又有四分一之加赋。以为转输夫马诸色之费。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今以此米谷。依朱子法。只取什二之息。则岁可得数百斛谷矣。以此充诸加赋之数。而正税之外零星科目。悉从蠲免。则民无大小。户无主客。均受其惠矣。且民常不免从豪右贷子母之息。而犹恐其不及。今什二者。息之最廉。而又免奔走候伺。得秕偿凿之弊矣。春而散以济其急。秋而敛以助其税。而又稍振其馀。储蓄既饶。然后一依朱子所定条约而行之。则施益广而所济益众矣。然吾特发其端而已。若其讨论而损益。世守而不坠。则在耆老诸君。盍以朱子之心为心。而相与勉之哉。咸序应曰诺。遂委其事于郭丈志仁,忠义卫李翊邦,别坐郑溭,进士李复初,郭廷瑗诸人。余亦忝随诸人之后。与闻绪论。而未几西归则卒不得承事。而诸人尽心殚诚。行之数年。实惠之及民者。不可选记矣。岁壬辰闵学士鼎重大受奉命。前后廉察两湖。习闻其事而善之。为写其条约一通。还朝引朱子乞行社仓议。亟请颁行于国中。以广国家周穷恤匮之意。且贤郭丈之为人。请加礼 召。益讲利病。俾得行之无弊。 上下其议于庙堂。顾以多事而未遑也。余
莫重于沃。盖正税之外。又有四分一之加赋。以为转输夫马诸色之费。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今以此米谷。依朱子法。只取什二之息。则岁可得数百斛谷矣。以此充诸加赋之数。而正税之外零星科目。悉从蠲免。则民无大小。户无主客。均受其惠矣。且民常不免从豪右贷子母之息。而犹恐其不及。今什二者。息之最廉。而又免奔走候伺。得秕偿凿之弊矣。春而散以济其急。秋而敛以助其税。而又稍振其馀。储蓄既饶。然后一依朱子所定条约而行之。则施益广而所济益众矣。然吾特发其端而已。若其讨论而损益。世守而不坠。则在耆老诸君。盍以朱子之心为心。而相与勉之哉。咸序应曰诺。遂委其事于郭丈志仁,忠义卫李翊邦,别坐郑溭,进士李复初,郭廷瑗诸人。余亦忝随诸人之后。与闻绪论。而未几西归则卒不得承事。而诸人尽心殚诚。行之数年。实惠之及民者。不可选记矣。岁壬辰闵学士鼎重大受奉命。前后廉察两湖。习闻其事而善之。为写其条约一通。还朝引朱子乞行社仓议。亟请颁行于国中。以广国家周穷恤匮之意。且贤郭丈之为人。请加礼 召。益讲利病。俾得行之无弊。 上下其议于庙堂。顾以多事而未遑也。余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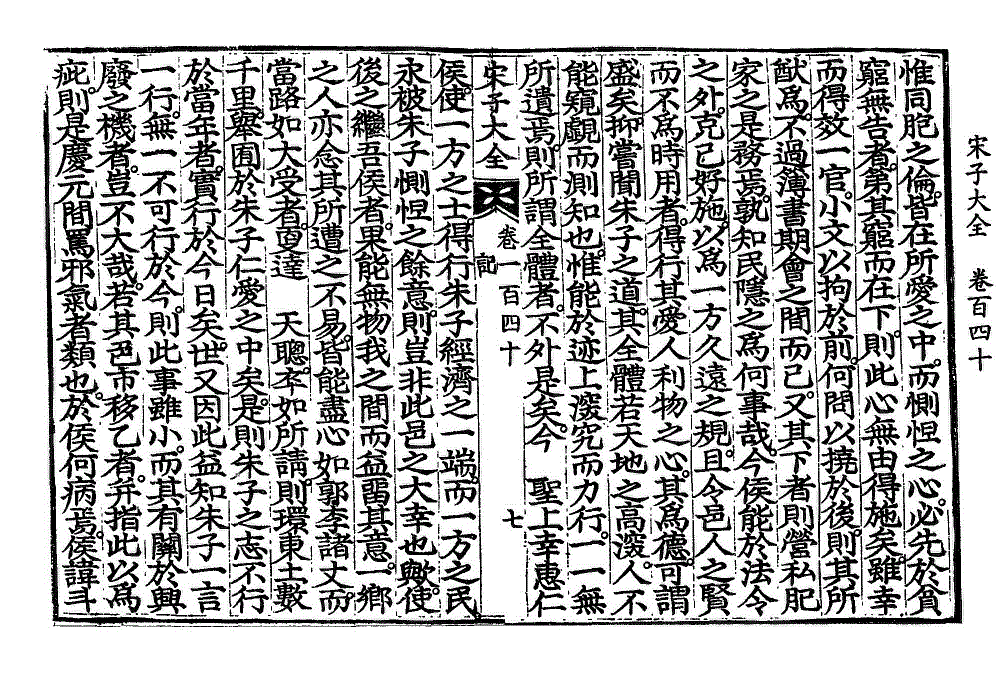 惟同胞之伦。皆在所爱之中。而恻怛之心。必先于贫穷无告者。第其穷而在下。则此心无由得施矣。虽幸而得效一官。小文以拘于前。何问以挠于后。则其所猷为。不过簿书期会之间而已。又其下者则营私肥家之是务焉。孰知民隐之为何事哉。今侯能于法令之外。克己好施。以为一方久远之规。且令邑人之贤而不为时用者。得行其爱人利物之心。其为德。可谓盛矣。抑尝闻朱子之道。其全体若天地之高深。人不能窥觑而测知也。惟能于迹上深究而力行。一一无所遗焉。则所谓全体者。不外是矣。今 圣上幸惠仁侯。使一方之士。得行朱子经济之一端。而一方之民。永被朱子恻怛之馀意。则岂非此邑之大幸也欤。使后之继吾侯者。果能无物我之间而益留其意。一乡之人亦念其所遭之不易。皆能尽心如郭,李诸丈。而当路如大受者。更达 天聪。卒如所请。则环东土数千里。举囿于朱子仁爱之中矣。是则朱子之志不行于当年者。实行于今日矣。世又因此益知朱子一言一行。无一不可行于今。则此事虽小。而其有关于兴废之机者。岂不大哉。若其色市移乙者。并指此以为疵。则是庆元间骂邪气者类也。于侯何病焉。侯讳斗
惟同胞之伦。皆在所爱之中。而恻怛之心。必先于贫穷无告者。第其穷而在下。则此心无由得施矣。虽幸而得效一官。小文以拘于前。何问以挠于后。则其所猷为。不过簿书期会之间而已。又其下者则营私肥家之是务焉。孰知民隐之为何事哉。今侯能于法令之外。克己好施。以为一方久远之规。且令邑人之贤而不为时用者。得行其爱人利物之心。其为德。可谓盛矣。抑尝闻朱子之道。其全体若天地之高深。人不能窥觑而测知也。惟能于迹上深究而力行。一一无所遗焉。则所谓全体者。不外是矣。今 圣上幸惠仁侯。使一方之士。得行朱子经济之一端。而一方之民。永被朱子恻怛之馀意。则岂非此邑之大幸也欤。使后之继吾侯者。果能无物我之间而益留其意。一乡之人亦念其所遭之不易。皆能尽心如郭,李诸丈。而当路如大受者。更达 天聪。卒如所请。则环东土数千里。举囿于朱子仁爱之中矣。是则朱子之志不行于当年者。实行于今日矣。世又因此益知朱子一言一行。无一不可行于今。则此事虽小。而其有关于兴废之机者。岂不大哉。若其色市移乙者。并指此以为疵。则是庆元间骂邪气者类也。于侯何病焉。侯讳斗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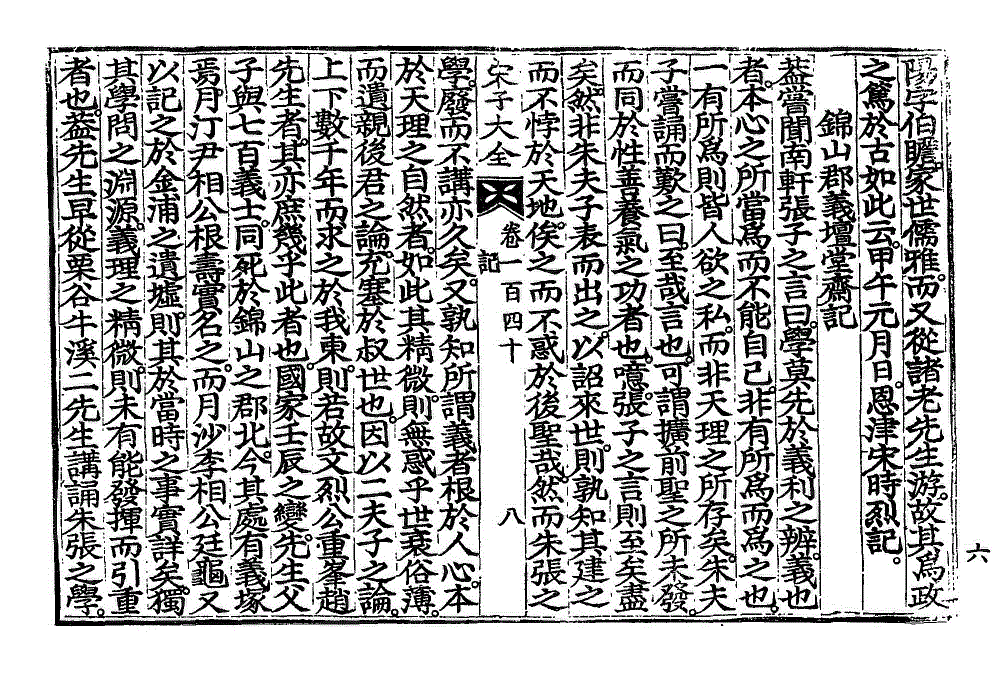 阳字伯瞻。家世儒雅。而又从诸老先生游。故其为政之笃于古如此云。甲午元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阳字伯瞻。家世儒雅。而又从诸老先生游。故其为政之笃于古如此云。甲午元月日。恩津宋时烈记。锦山郡义坛堂斋记
盖尝闻南轩张子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也。一有所为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夫子尝诵而叹之曰。至哉言也。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也。噫。张子之言则至矣尽矣。然非朱夫子表而出之。以诏来世。则孰知其建之而不悖于天地。俟之而不惑于后圣哉。然而朱张之学。废而不讲亦久矣。又孰知所谓义者根于人心。本于天理之自然者。如此其精微。则无惑乎世衰俗薄。而遗亲后君之论。充塞于叔世也。因以二夫子之论。上下数千年而求之于我东。则若故文烈公重峰赵先生者。其亦庶几乎此者也。国家壬辰之变。先生父子与七百义士。同死于锦山之郡北。今其处有义冢焉。月汀尹相公根寿实名之。而月沙李相公廷龟又以记之于金浦之遗墟。则其于当时之事实详矣。独其学问之渊源。义理之精微。则未有能发挥而引重者也。盖先生早从栗谷,牛溪二先生讲诵朱张之学。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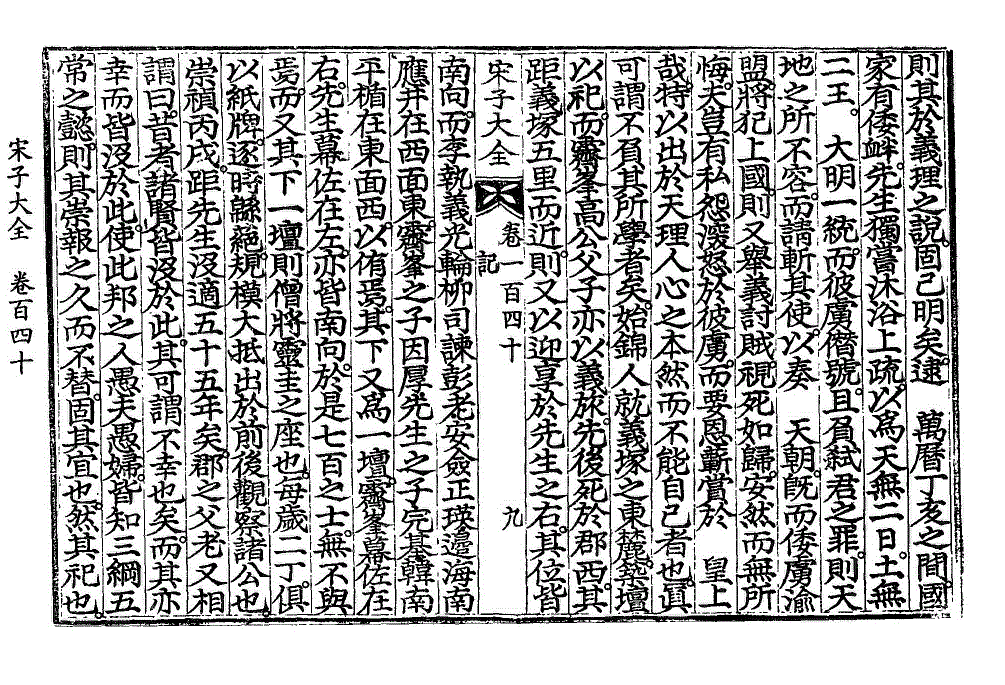 则其于义理之说。固已明矣。逮 万历丁亥之间。国家有倭衅。先生独尝沐浴上疏。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大明一统。而彼虏僭号。且负弑君之罪。则天地之所不容。而请斩其使。以奏 天朝。既而倭虏渝盟。将犯上国。则又举义讨贼。视死如归。安然而无所悔。夫岂有私怨深怒于彼虏。而要恩蕲赏于 皇上哉。特以出于天理人心之本然而不能自已者也。真可谓不负其所学者矣。始锦人就义冢之东麓。筑坛以祀。而霁峰高公父子亦以义旅。先后死于郡西。其距义冢五里而近。则又以迎享于先生之右。其位皆南向。而李执义光轮,柳司谏彭老,安佥正瑛,边海南应井在西面东。霁峰之子因厚,先生之子完基,韩南平楯在东面西。以侑焉。其下又为一坛。霁峰幕佐在右。先生幕佐在左。亦皆南向。于是七百之士。无不与焉。而又其下一坛则僧将灵圭之座也。每岁二丁。俱以纸牌。逐时绵蕝。规模大抵出于前后观察诸公也。崇祯丙戌。距先生没适五十五年矣。郡之父老又相谓曰。昔者诸贤皆没于此。其可谓不幸也矣。而其亦幸而皆没于此。使此邦之人愚夫愚妇。皆知三纲五常之懿。则其崇报之久而不替。固其宜也。然其祀也。
则其于义理之说。固已明矣。逮 万历丁亥之间。国家有倭衅。先生独尝沐浴上疏。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大明一统。而彼虏僭号。且负弑君之罪。则天地之所不容。而请斩其使。以奏 天朝。既而倭虏渝盟。将犯上国。则又举义讨贼。视死如归。安然而无所悔。夫岂有私怨深怒于彼虏。而要恩蕲赏于 皇上哉。特以出于天理人心之本然而不能自已者也。真可谓不负其所学者矣。始锦人就义冢之东麓。筑坛以祀。而霁峰高公父子亦以义旅。先后死于郡西。其距义冢五里而近。则又以迎享于先生之右。其位皆南向。而李执义光轮,柳司谏彭老,安佥正瑛,边海南应井在西面东。霁峰之子因厚,先生之子完基,韩南平楯在东面西。以侑焉。其下又为一坛。霁峰幕佐在右。先生幕佐在左。亦皆南向。于是七百之士。无不与焉。而又其下一坛则僧将灵圭之座也。每岁二丁。俱以纸牌。逐时绵蕝。规模大抵出于前后观察诸公也。崇祯丙戌。距先生没适五十五年矣。郡之父老又相谓曰。昔者诸贤皆没于此。其可谓不幸也矣。而其亦幸而皆没于此。使此邦之人愚夫愚妇。皆知三纲五常之懿。则其崇报之久而不替。固其宜也。然其祀也。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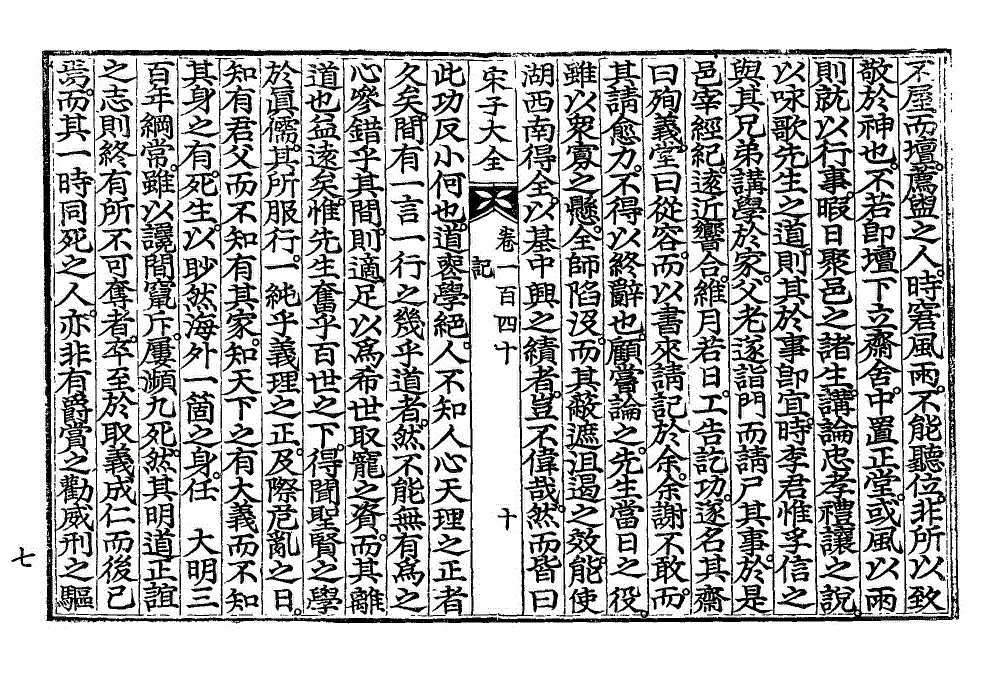 不屋而坛。荐盥之人。时窘风雨。不能听位。非所以致敬于神也。不若即坛下立斋舍。中置正堂。或风以雨则就以行事。暇日聚邑之诸生。讲论忠孝礼让之说。以咏歌先生之道。则其于事即宜。时李君惟孚信之与其兄弟讲学于家。父老遂诣门而请尸其事。于是邑宰经纪。远近响合。维月若日。工告讫功。遂名其斋曰殉义。堂曰从容。而以书来请记于余。余谢不敢。而其请愈力。不得以终辞也。顾尝论之。先生当日之役。虽以众寡之悬。全师陷没。而其蔽遮沮遏之效。能使湖西南得全。以基中兴之绩者。岂不伟哉。然而皆曰此功反小何也。道丧学绝。人不知人心天理之正者久矣。间有一言一行之几乎道者。然不能无有为之心参错乎其间。则适足以为希世取宠之资。而其离道也益远矣。惟先生奋乎百世之下。得闻圣贤之学于真儒。其所服行。一纯乎义理之正。及际危乱之日。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家。知天下之有大义而不知其身之有。死生。以眇然海外一个之身。任 大明三百年纲常。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然其明道正谊之志则终有所不可夺者。卒至于取义成仁而后已焉。而其一时同死之人。亦非有爵赏之劝威刑之驱
不屋而坛。荐盥之人。时窘风雨。不能听位。非所以致敬于神也。不若即坛下立斋舍。中置正堂。或风以雨则就以行事。暇日聚邑之诸生。讲论忠孝礼让之说。以咏歌先生之道。则其于事即宜。时李君惟孚信之与其兄弟讲学于家。父老遂诣门而请尸其事。于是邑宰经纪。远近响合。维月若日。工告讫功。遂名其斋曰殉义。堂曰从容。而以书来请记于余。余谢不敢。而其请愈力。不得以终辞也。顾尝论之。先生当日之役。虽以众寡之悬。全师陷没。而其蔽遮沮遏之效。能使湖西南得全。以基中兴之绩者。岂不伟哉。然而皆曰此功反小何也。道丧学绝。人不知人心天理之正者久矣。间有一言一行之几乎道者。然不能无有为之心参错乎其间。则适足以为希世取宠之资。而其离道也益远矣。惟先生奋乎百世之下。得闻圣贤之学于真儒。其所服行。一纯乎义理之正。及际危乱之日。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家。知天下之有大义而不知其身之有。死生。以眇然海外一个之身。任 大明三百年纲常。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然其明道正谊之志则终有所不可夺者。卒至于取义成仁而后已焉。而其一时同死之人。亦非有爵赏之劝威刑之驱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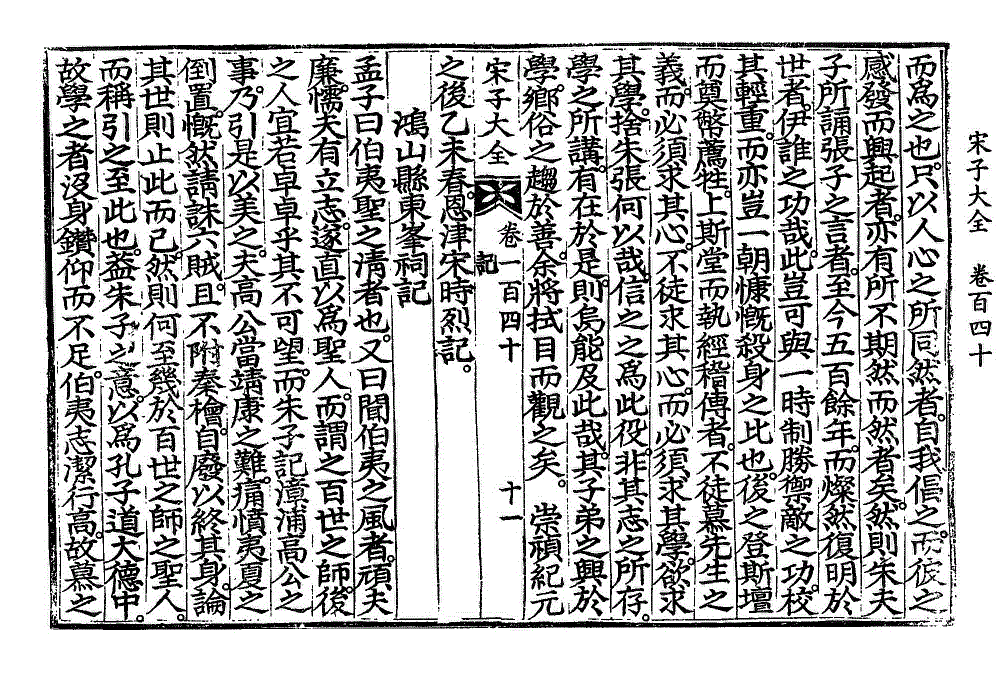 而为之也。只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倡之。而彼之感发而兴起者。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矣。然则朱夫子所诵张子之言者。至今五百馀年。而灿然复明于世者。伊谁之功哉。此岂可与一时制胜御敌之功。校其轻重。而亦岂一朝慷慨杀身之比也。后之登斯坛而奠币荐牲。上斯堂而执经稽传者。不徒慕先生之义。而必须求其心。不徒求其心。而必须求其学。欲求其学。舍朱张何以哉。信之之为此役。非其志之所存。学之所讲。有在于是。则乌能及此哉。其子弟之兴于学。乡俗之趋于善。余将拭目而观之矣。 崇祯纪元之后乙未春。恩津宋时烈记。
而为之也。只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倡之。而彼之感发而兴起者。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矣。然则朱夫子所诵张子之言者。至今五百馀年。而灿然复明于世者。伊谁之功哉。此岂可与一时制胜御敌之功。校其轻重。而亦岂一朝慷慨杀身之比也。后之登斯坛而奠币荐牲。上斯堂而执经稽传者。不徒慕先生之义。而必须求其心。不徒求其心。而必须求其学。欲求其学。舍朱张何以哉。信之之为此役。非其志之所存。学之所讲。有在于是。则乌能及此哉。其子弟之兴于学。乡俗之趋于善。余将拭目而观之矣。 崇祯纪元之后乙未春。恩津宋时烈记。鸿山县东峰祠记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又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遂直以为圣人。而谓之百世之师。后之人宜若卓卓乎其不可望。而朱子记漳浦高公之事。乃引是以美之。夫高公当靖康之难。痛愤夷夏之倒置。慨然请诛六贼。且不附秦桧。自废以终其身。论其世则止此而已。然则何至几于百世之师之圣人。而称引之至此也。盖朱子之意。以为孔子道大德中。故学之者没身钻仰而不足。伯夷志洁行高。故慕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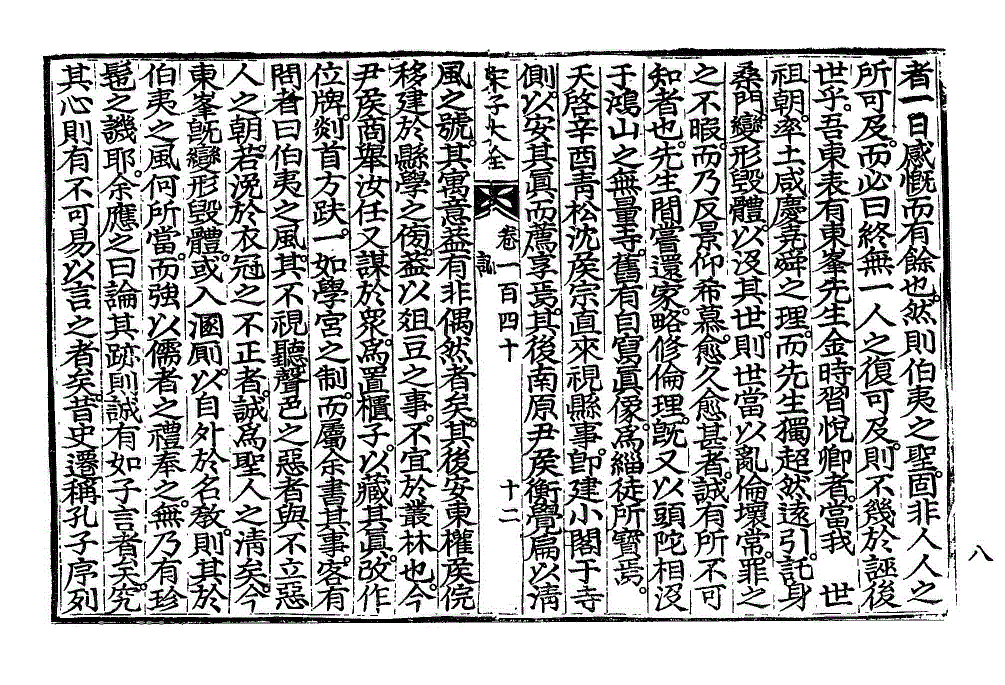 者一日感慨而有馀也。然则伯夷之圣。固非人人之所可及。而必曰终无一人之复可及。则不几于诬后世乎。吾东表有东峰先生金时习悦卿者。当我 世祖朝。率土咸庆尧舜之理。而先生独超然远引。托身桑门。变形毁体。以没其世。则世当以乱伦坏常。罪之之不暇。而乃反景仰希慕。愈久愈甚者。诚有所不可知者也。先生间尝还家。略修伦理。既又以头陀相没于鸿山之无量寺。旧有自写真像。为缁徒所宝焉。 天启辛酉青松沈侯宗直来视县事。即建小阁于寺侧。以安其真而荐享焉。其后南原尹侯衡觉扁以清风之号。其寓意盖有非偶然者矣。其后安东权侯俒移建于县学之傍。盖以俎豆之事。不宜于丛林也。今尹侯商举汝任又谋于众。为置匮子。以藏其真。改作位牌。剡首方趺。一如学宫之制。而属余书其事。客有问者曰伯夷之风。其不视听声色之恶者与不立恶人之朝。若浼于衣冠之不正者。诚为圣人之清矣。今东峰既变形毁体。或入溷厕。以自外于名教。则其于伯夷之风何所当。而强以儒者之礼奉之。无乃有珍剃之讥耶。余应之曰论其迹则诚有如子言者矣。究其心则有不可易以言之者矣。昔史迁称孔子序列
者一日感慨而有馀也。然则伯夷之圣。固非人人之所可及。而必曰终无一人之复可及。则不几于诬后世乎。吾东表有东峰先生金时习悦卿者。当我 世祖朝。率土咸庆尧舜之理。而先生独超然远引。托身桑门。变形毁体。以没其世。则世当以乱伦坏常。罪之之不暇。而乃反景仰希慕。愈久愈甚者。诚有所不可知者也。先生间尝还家。略修伦理。既又以头陀相没于鸿山之无量寺。旧有自写真像。为缁徒所宝焉。 天启辛酉青松沈侯宗直来视县事。即建小阁于寺侧。以安其真而荐享焉。其后南原尹侯衡觉扁以清风之号。其寓意盖有非偶然者矣。其后安东权侯俒移建于县学之傍。盖以俎豆之事。不宜于丛林也。今尹侯商举汝任又谋于众。为置匮子。以藏其真。改作位牌。剡首方趺。一如学宫之制。而属余书其事。客有问者曰伯夷之风。其不视听声色之恶者与不立恶人之朝。若浼于衣冠之不正者。诚为圣人之清矣。今东峰既变形毁体。或入溷厕。以自外于名教。则其于伯夷之风何所当。而强以儒者之礼奉之。无乃有珍剃之讥耶。余应之曰论其迹则诚有如子言者矣。究其心则有不可易以言之者矣。昔史迁称孔子序列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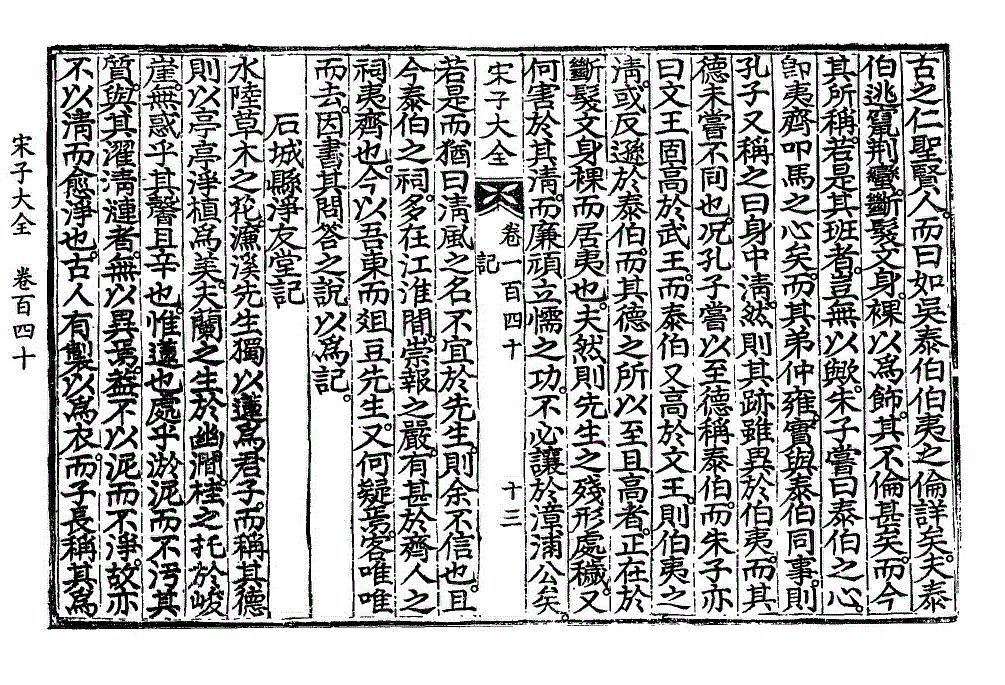 古之仁圣贤人。而曰如吴泰伯,伯夷之伦详矣。夫泰伯逃窜荆蛮。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其不伦甚矣。而今其所称。若是其班者。岂无以欤。朱子尝曰泰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矣。而其弟仲雍。实与泰伯同事。则孔子又称之曰身中清。然则其迹虽异于伯夷。而其德未尝不同也。况孔子尝以至德称泰伯。而朱子亦曰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又高于文王。则伯夷之清。或反逊于泰伯。而其德之所以至且高者。正在于断发文身裸而居夷也。夫然则先生之残形处秽。又何害于其清。而廉顽立懦之功。不必让于漳浦公矣。若是而犹曰清风之名不宜于先生。则余不信也。且今泰伯之祠。多在江淮间。崇报之严。有甚于齐人之祠夷齐也。今以吾东而俎豆先生。又何疑焉。客唯唯而去。因书其问答之说以为记。
古之仁圣贤人。而曰如吴泰伯,伯夷之伦详矣。夫泰伯逃窜荆蛮。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其不伦甚矣。而今其所称。若是其班者。岂无以欤。朱子尝曰泰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矣。而其弟仲雍。实与泰伯同事。则孔子又称之曰身中清。然则其迹虽异于伯夷。而其德未尝不同也。况孔子尝以至德称泰伯。而朱子亦曰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又高于文王。则伯夷之清。或反逊于泰伯。而其德之所以至且高者。正在于断发文身裸而居夷也。夫然则先生之残形处秽。又何害于其清。而廉顽立懦之功。不必让于漳浦公矣。若是而犹曰清风之名不宜于先生。则余不信也。且今泰伯之祠。多在江淮间。崇报之严。有甚于齐人之祠夷齐也。今以吾东而俎豆先生。又何疑焉。客唯唯而去。因书其问答之说以为记。石城县净友堂记
水陆草木之花。濂溪先生独以莲为君子。而称其德则以亭亭净植为美。夫兰之生于幽涧。桂之托于峻崖。无惑乎其馨且辛也。惟莲也处乎淤泥而不污其质。与其濯清涟者。无以异焉。盖不以泥而不净。故亦不以清而愈净也。古人有制以为衣。而子长称其为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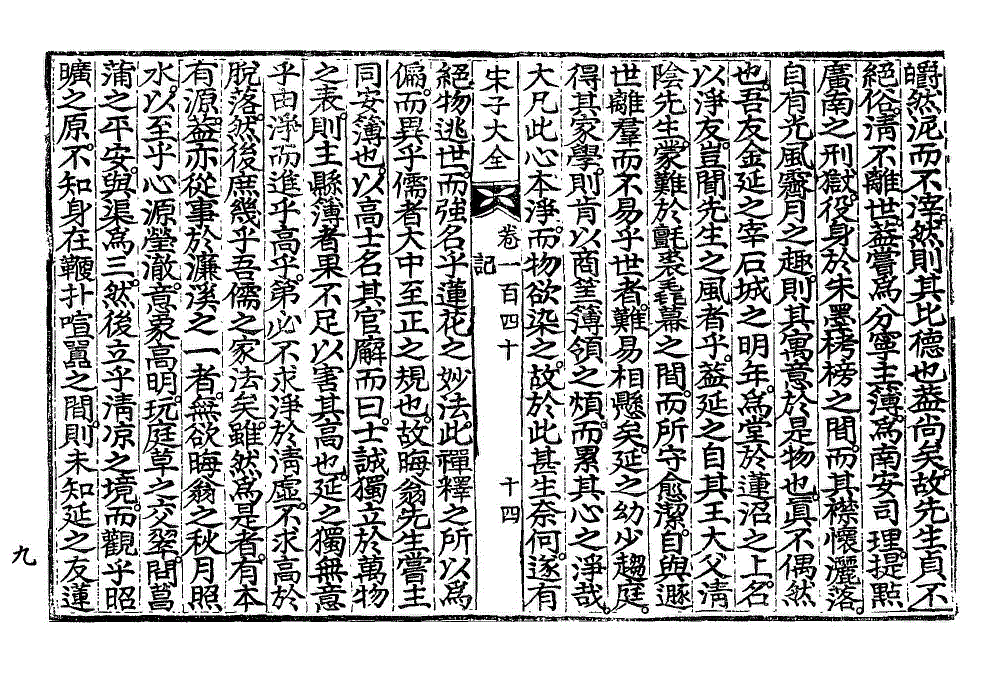 皭然泥而不滓。然则其比德也盖尚矣。故先生贞不绝俗。清不离世。盖尝为分宁主簿。为南安司理。提点广南之刑狱。役身于朱墨栲榜之间。而其襟怀洒落。自有光风霁月之趣。则其寓意于是物也。真不偶然也。吾友金延之宰石城之明年。为堂于莲沼之上。名以净友。岂闻先生之风者乎。盖延之自其王大父清阴先生。蒙难于毡裘毳幕之间。而所守愈洁。自与遁世离群而不易乎世者。难易相悬矣。延之幼少趋庭。得其家学。则肯以商算簿领之烦。而累其心之净哉。大凡此心本净。而物欲染之。故于此甚生奈何。遂有绝物逃世。而强名乎莲花之妙法。此禅释之所以为偏。而异乎儒者大中至正之规也。故晦翁先生尝主同安簿也。以高士名其官廨而曰。士诚独立于万物之表。则主县簿者果不足以害其高也。延之独无意乎由净而进乎高乎。第必不求净于清虚。不求高于脱落。然后庶几乎吾儒之家法矣。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源。盖亦从事于濂溪之一者。无欲晦翁之秋月照水。以至乎心源莹澈。意象高明。玩庭草之交翠。问菖蒲之平安。与渠为三。然后立乎清凉之境。而观乎昭旷之原。不知身在鞭扑喧嚣之间。则未知延之友莲
皭然泥而不滓。然则其比德也盖尚矣。故先生贞不绝俗。清不离世。盖尝为分宁主簿。为南安司理。提点广南之刑狱。役身于朱墨栲榜之间。而其襟怀洒落。自有光风霁月之趣。则其寓意于是物也。真不偶然也。吾友金延之宰石城之明年。为堂于莲沼之上。名以净友。岂闻先生之风者乎。盖延之自其王大父清阴先生。蒙难于毡裘毳幕之间。而所守愈洁。自与遁世离群而不易乎世者。难易相悬矣。延之幼少趋庭。得其家学。则肯以商算簿领之烦。而累其心之净哉。大凡此心本净。而物欲染之。故于此甚生奈何。遂有绝物逃世。而强名乎莲花之妙法。此禅释之所以为偏。而异乎儒者大中至正之规也。故晦翁先生尝主同安簿也。以高士名其官廨而曰。士诚独立于万物之表。则主县簿者果不足以害其高也。延之独无意乎由净而进乎高乎。第必不求净于清虚。不求高于脱落。然后庶几乎吾儒之家法矣。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源。盖亦从事于濂溪之一者。无欲晦翁之秋月照水。以至乎心源莹澈。意象高明。玩庭草之交翠。问菖蒲之平安。与渠为三。然后立乎清凉之境。而观乎昭旷之原。不知身在鞭扑喧嚣之间。则未知延之友莲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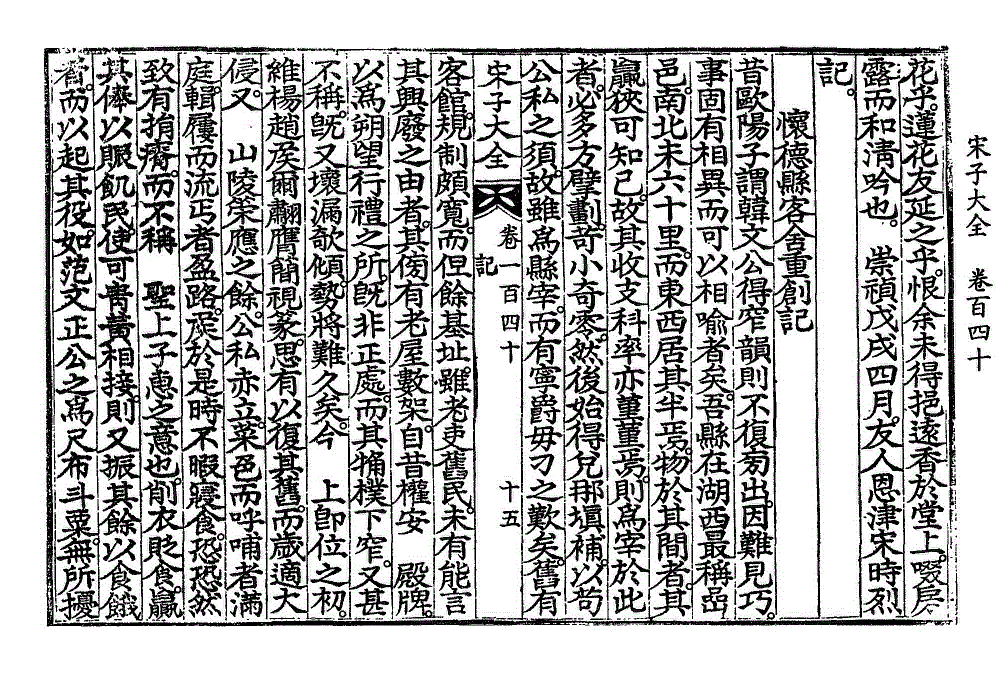 花乎。莲花友延之乎。恨余未得挹远香于堂上。啜房露而和清吟也。 崇祯戊戌四月。友人恩津宋时烈记。
花乎。莲花友延之乎。恨余未得挹远香于堂上。啜房露而和清吟也。 崇祯戊戌四月。友人恩津宋时烈记。怀德县客舍重创记
昔欧阳子谓韩文公得窄韵则不复旁出。因难见巧。事固有相异而可以相喻者矣。吾县在湖西最称岩邑。南北未六十里。而东西居其半焉。物于其间者。其赢狭可知已。故其收支科率亦堇堇焉。则为宰于此者。必多方擘划。苛小奇零。然后始得兑那填补。以苟公私之须。故虽为县宰。而有宁爵毋刁之叹矣。旧有客馆。规制颇宽。而但馀基址。虽老吏旧民。未有能言其兴废之由者。其傍有老屋数架。自昔权安 殿牌。以为朔望行礼之所。既非正处。而其觕朴下窄。又甚不称。既又坏漏欹倾。势将难久矣。今 上即位之初。维杨赵侯尔䎘膺简视篆。思有以复其旧。而岁适大侵。又 山陵策应之馀。公私赤立。菜色而呼哺者满庭。辑屦而流丐者盈路。侯于是时不暇寝食。恐恐然致有捐瘠。而不称 圣上子惠之意也。削衣贬食。赢其俸以赈饥民。使可青黄相接。则又振其馀以食饿者。而以起其役。如范文正公之为尺布斗粟。无所扰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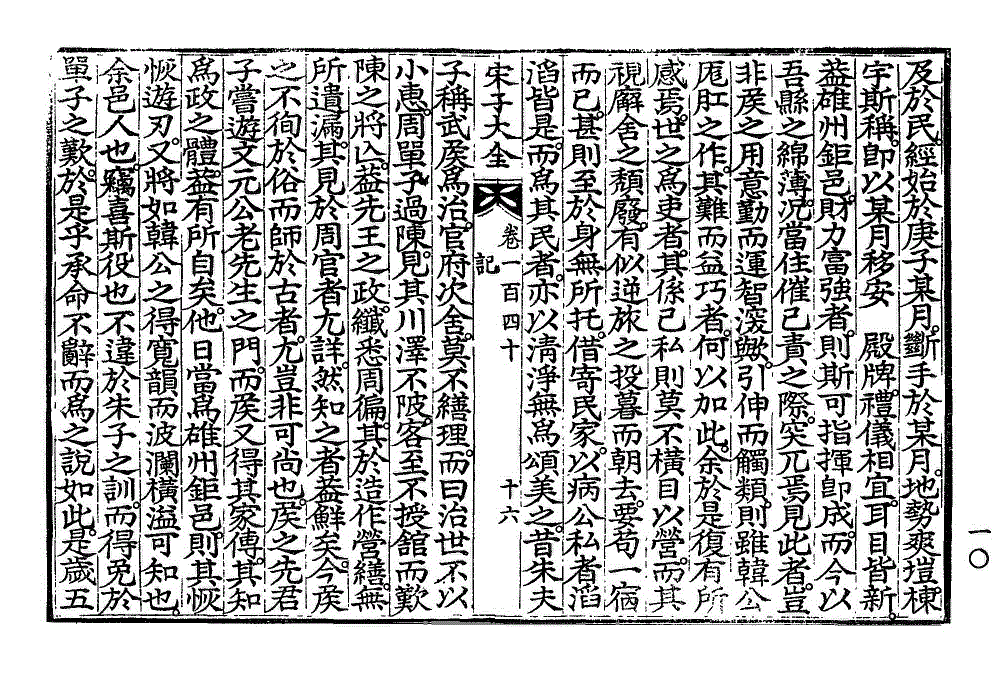 及于民。经始于庚子某月。断手于某月。地势爽垲。栋宇斯称。即以某月移安 殿牌。礼仪相宜。耳目皆新。盖雄州钜邑。财力富强者。则斯可指挥即成。而今以吾县之绵薄。况当住催己责之际。突兀焉见此者。岂非侯之用意勤而运智深欤。引伸而触类。则虽韩公厖肛之作。其难而益巧者。何以加此。余于是复有所感焉。世之为吏者。其系己私则莫不横目以营。而其视廨舍之颓废。有似逆旅之投暮而朝去。要苟一宿而已。甚则至于身无所托。借寄民家。以病公私者滔滔皆是。而为其民者。亦以清净无为颂美之。昔朱夫子称武侯为治。官府次舍。莫不缮理。而曰治世不以小惠。周单子过陈。见其川泽不陂。客至不授馆而叹陈之将亡。盖先王之政。纤悉周遍。其于造作营缮。无所遗漏。其见于周官者尤详。然知之者盖鲜矣。今侯之不徇于俗而师于古者。尤岂非可尚也。侯之先君子尝游文元公老先生之门。而侯又得其家传。其知为政之体。盖有所自矣。他日当为雄州钜邑。则其恢恢游刃。又将如韩公之得宽韵而波澜横溢可知也。余邑人也。窃喜斯役也不违于朱子之训。而得免于单子之叹。于是乎承命不辞而为之说如此。是岁五
及于民。经始于庚子某月。断手于某月。地势爽垲。栋宇斯称。即以某月移安 殿牌。礼仪相宜。耳目皆新。盖雄州钜邑。财力富强者。则斯可指挥即成。而今以吾县之绵薄。况当住催己责之际。突兀焉见此者。岂非侯之用意勤而运智深欤。引伸而触类。则虽韩公厖肛之作。其难而益巧者。何以加此。余于是复有所感焉。世之为吏者。其系己私则莫不横目以营。而其视廨舍之颓废。有似逆旅之投暮而朝去。要苟一宿而已。甚则至于身无所托。借寄民家。以病公私者滔滔皆是。而为其民者。亦以清净无为颂美之。昔朱夫子称武侯为治。官府次舍。莫不缮理。而曰治世不以小惠。周单子过陈。见其川泽不陂。客至不授馆而叹陈之将亡。盖先王之政。纤悉周遍。其于造作营缮。无所遗漏。其见于周官者尤详。然知之者盖鲜矣。今侯之不徇于俗而师于古者。尤岂非可尚也。侯之先君子尝游文元公老先生之门。而侯又得其家传。其知为政之体。盖有所自矣。他日当为雄州钜邑。则其恢恢游刃。又将如韩公之得宽韵而波澜横溢可知也。余邑人也。窃喜斯役也不违于朱子之训。而得免于单子之叹。于是乎承命不辞而为之说如此。是岁五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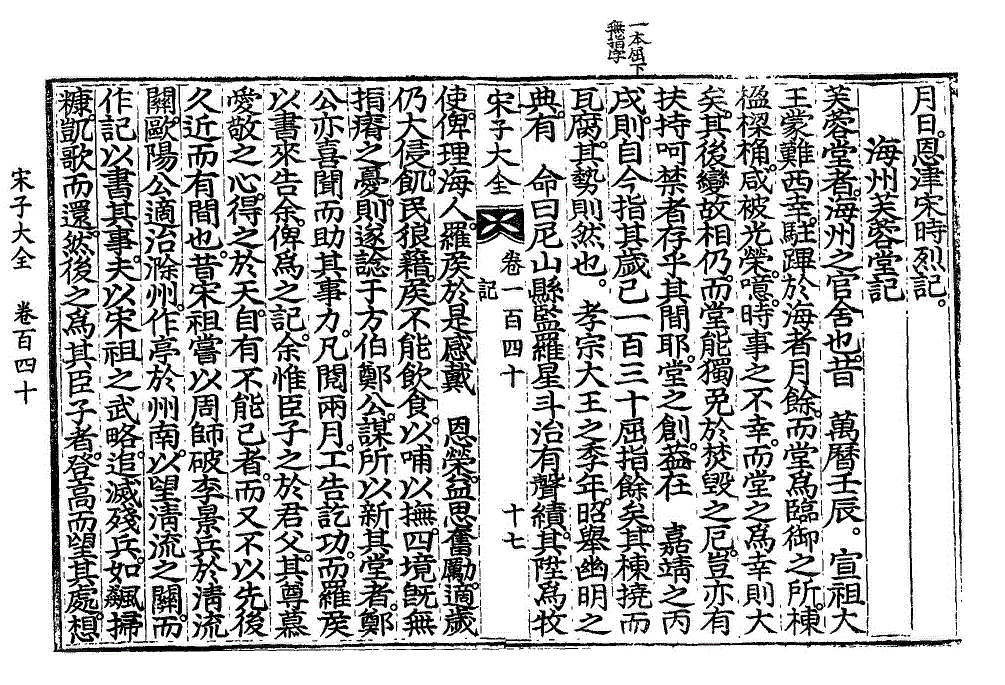 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月日。恩津宋时烈记。海州芙蓉堂记
芙蓉堂者。海州之官舍也。昔 万历壬辰。 宣祖大王蒙难西幸。驻跸于海者月馀。而堂为临御之所。栋楹梁桷。咸被光荣。噫。时事之不幸。而堂之为幸则大矣。其后变故相仍。而堂能独免于焚毁之厄。岂亦有扶持呵禁者存乎其间耶。堂之创。盖在 嘉靖之丙戌。则自今指其岁已一百三十屈(一本屈下无指字)指馀矣。其栋挠而瓦腐。其势则然也。 孝宗大王之季年。昭举幽明之典。有 命曰尼山县监罗星斗治有声绩。其升为牧使。俾理海人。罗侯于是感戴 恩荣。益思奋励。适岁仍大侵。饥民狼藉。侯不能饮食。以哺以抚。四境既无捐瘠之忧。则遂谂于方伯郑公。谋所以新其堂者。郑公亦喜闻而助其事力。凡阅两月。工告讫功。而罗侯以书来告余。俾为之记。余惟臣子之于君父。其尊慕爱敬之心。得之于天。自有不能已者。而又不以先后久近而有间也。昔宋祖尝以周师破李景兵于清流关。欧阳公适治滁州。作亭于州南。以望清流之关。而作记以书其事。夫以宋祖之武略。追灭残兵。如飙扫糠。凯歌而还。然后之为其臣子者。登高而望其处。想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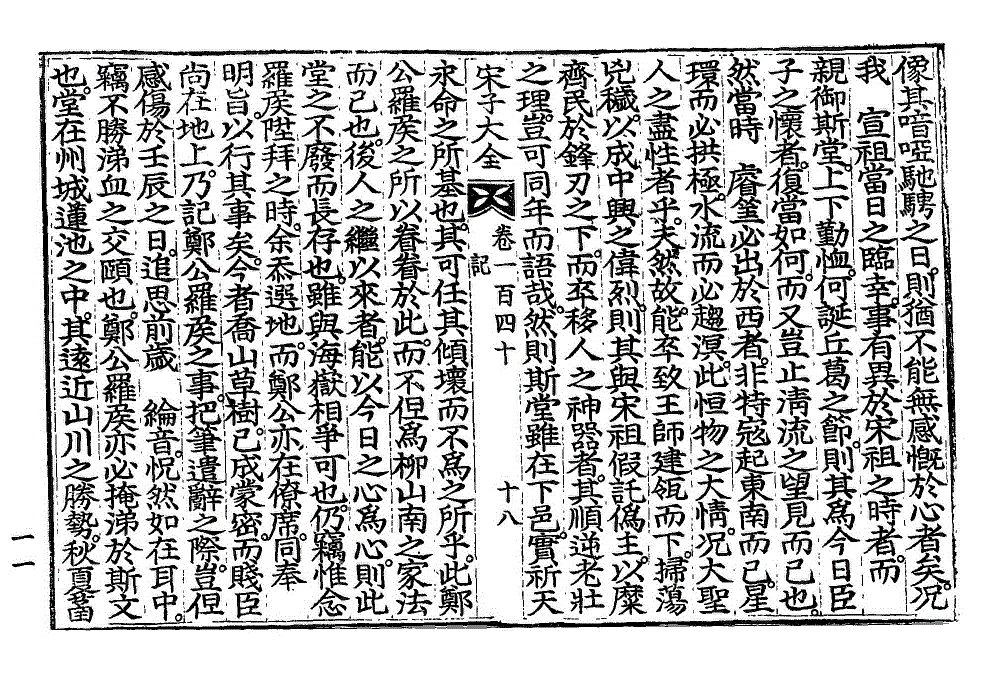 像其喑哑驰骋之日。则犹不能无感慨于心者矣。况我 宣祖当日之临幸。事有异于宋祖之时者。而 亲御斯堂。上下勤恤。何诞丘葛之节。则其为今日臣子之怀者。复当如何。而又岂止清流之望见而已也。然当时 睿算必出于西者。非特寇起东南而已。星环而必拱极。水流而必趋溟。此恒物之大情。况大圣人之尽性者乎。夫然故。能卒致王师建瓴而下。扫荡凶秽。以成中兴之伟烈。则其与宋祖假托伪主。以糜齐民于锋刃之下。而卒移人之神器者。其顺逆老壮之理。岂可同年而语哉。然则斯堂虽在下邑。实祈天永命之所基也。其可任其倾坏而不为之所乎。此郑公罗侯之所以眷眷于此。而不但为柳山南之家法而已也。后人之继以来者。能以今日之心为心。则此堂之不废而长存也。虽与海岳相争可也。仍窃惟念罗侯升拜之时。余忝选地。而郑公亦在僚席。同奉 明旨。以行其事矣。今者乔山草树。已成蒙密。而贱臣尚在地上。乃记郑公罗侯之事。把笔遣辞之际。岂但感伤于壬辰之日。追思前岁 纶音。恍然如在耳中。窃不胜涕血之交颐也。郑公罗侯亦必掩涕于斯文也。堂在州城莲池之中。其远近山川之胜势。秋夏菡
像其喑哑驰骋之日。则犹不能无感慨于心者矣。况我 宣祖当日之临幸。事有异于宋祖之时者。而 亲御斯堂。上下勤恤。何诞丘葛之节。则其为今日臣子之怀者。复当如何。而又岂止清流之望见而已也。然当时 睿算必出于西者。非特寇起东南而已。星环而必拱极。水流而必趋溟。此恒物之大情。况大圣人之尽性者乎。夫然故。能卒致王师建瓴而下。扫荡凶秽。以成中兴之伟烈。则其与宋祖假托伪主。以糜齐民于锋刃之下。而卒移人之神器者。其顺逆老壮之理。岂可同年而语哉。然则斯堂虽在下邑。实祈天永命之所基也。其可任其倾坏而不为之所乎。此郑公罗侯之所以眷眷于此。而不但为柳山南之家法而已也。后人之继以来者。能以今日之心为心。则此堂之不废而长存也。虽与海岳相争可也。仍窃惟念罗侯升拜之时。余忝选地。而郑公亦在僚席。同奉 明旨。以行其事矣。今者乔山草树。已成蒙密。而贱臣尚在地上。乃记郑公罗侯之事。把笔遣辞之际。岂但感伤于壬辰之日。追思前岁 纶音。恍然如在耳中。窃不胜涕血之交颐也。郑公罗侯亦必掩涕于斯文也。堂在州城莲池之中。其远近山川之胜势。秋夏菡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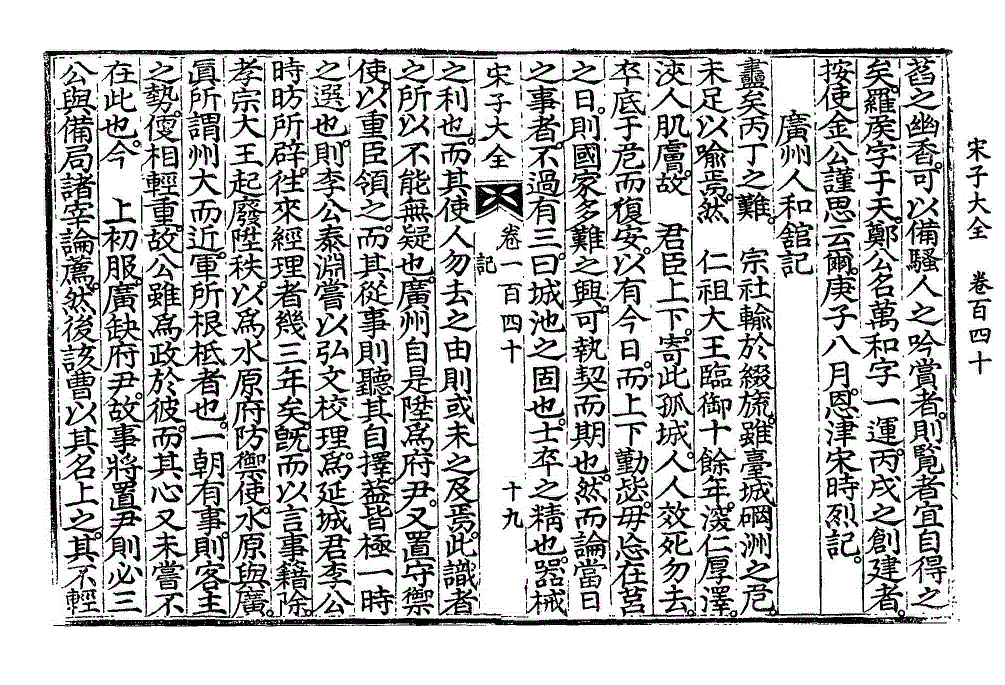 萏之幽香。可以备骚人之吟赏者。则览者宜自得之矣。罗侯字于天。郑公名万和字一运。丙戌之创建者。按使金公谨思云尔。庚子八月。恩津宋时烈记。
萏之幽香。可以备骚人之吟赏者。则览者宜自得之矣。罗侯字于天。郑公名万和字一运。丙戌之创建者。按使金公谨思云尔。庚子八月。恩津宋时烈记。广州人和馆记
衋矣丙丁之难。 宗社输于缀旒。虽台城䃃洲之危。未足以喻焉。然 仁祖大王临御十馀年。深仁厚泽。浃人肌肤。故 君臣上下。寄此孤城。人人效死勿去。卒底于危而复安。以有今日。而上下勤毖。毋忘在莒之日。则国家多难之兴。可执契而期也。然而论当日之事者。不过有三。曰城池之固也。士卒之精也。器械之利也。而其使人勿去之由则或未之及焉。此识者之所以不能无疑也。广州自是升为府尹。又置守御使。以重臣领之。而其从事则听其自择。盖皆极一时之选也。则李公泰渊尝以弘文校理。为延城君李公时昉所辟。往来经理者几三年矣。既而以言事籍除。孝宗大王起废升秩。以为水原府防御使。水原与广。真所谓州大而近。军所根柢者也。一朝有事。则客主之势。便相轻重。故公虽为政于彼。而其心又未尝不在此也。今 上初服。广缺府尹。故事将置尹则必三公与备局诸宰论荐。然后该曹以其名上之。其不轻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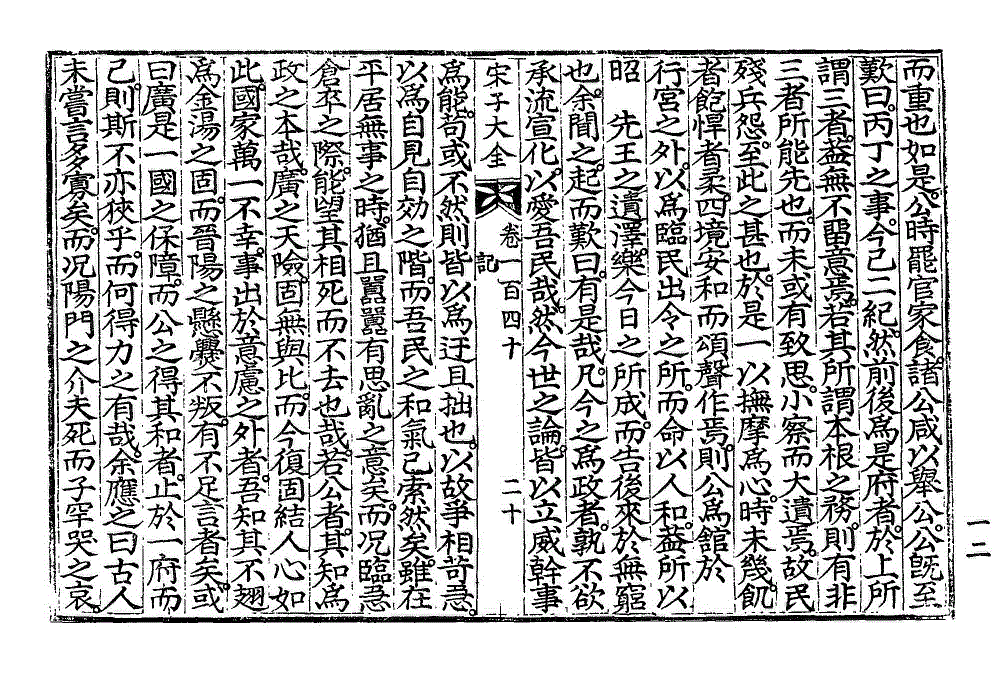 而重也如是。公时罢官家食。诸公咸以举公。公既至叹曰。丙丁之事。今已二纪。然前后为是府者。于上所谓三者。盖无不留意焉。若其所谓本根之务。则有非三者所能先也。而未或有致思。小察而大遗焉。故民残兵怨。至此之甚也。于是一以抚摩为心。时未几。饥者饱悍者柔。四境安和而颂声作焉。则公为馆于 行宫之外。以为临民出令之所。而命以人和。盖所以昭 先王之遗泽。乐今日之所成。而告后来于无穷也。余闻之。起而叹曰。有是哉。凡今之为政者。孰不欲承流宣化。以爱吾民哉。然今世之论。皆以立威干事为能。苟或不然则皆以为迂且拙也。以故争相苛急。以为自见自效之阶。而吾民之和气已索然矣。虽在平居无事之时。犹且嚣嚣有思乱之意矣。而况临急仓卒之际。能望其相死而不去也哉。若公者。其知为政之本哉。广之天险。固无与比。而今复固结人心如此。国家万一不幸。事出于意虑之外者。吾知其不翅为金汤之固。而晋阳之悬爨不叛。有不足言者矣。或曰广是一国之保障。而公之得其和者。止于一府而已。则斯不亦狭乎。而何得力之有哉。余应之曰古人未尝言多寡矣。而况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
而重也如是。公时罢官家食。诸公咸以举公。公既至叹曰。丙丁之事。今已二纪。然前后为是府者。于上所谓三者。盖无不留意焉。若其所谓本根之务。则有非三者所能先也。而未或有致思。小察而大遗焉。故民残兵怨。至此之甚也。于是一以抚摩为心。时未几。饥者饱悍者柔。四境安和而颂声作焉。则公为馆于 行宫之外。以为临民出令之所。而命以人和。盖所以昭 先王之遗泽。乐今日之所成。而告后来于无穷也。余闻之。起而叹曰。有是哉。凡今之为政者。孰不欲承流宣化。以爱吾民哉。然今世之论。皆以立威干事为能。苟或不然则皆以为迂且拙也。以故争相苛急。以为自见自效之阶。而吾民之和气已索然矣。虽在平居无事之时。犹且嚣嚣有思乱之意矣。而况临急仓卒之际。能望其相死而不去也哉。若公者。其知为政之本哉。广之天险。固无与比。而今复固结人心如此。国家万一不幸。事出于意虑之外者。吾知其不翅为金汤之固。而晋阳之悬爨不叛。有不足言者矣。或曰广是一国之保障。而公之得其和者。止于一府而已。则斯不亦狭乎。而何得力之有哉。余应之曰古人未尝言多寡矣。而况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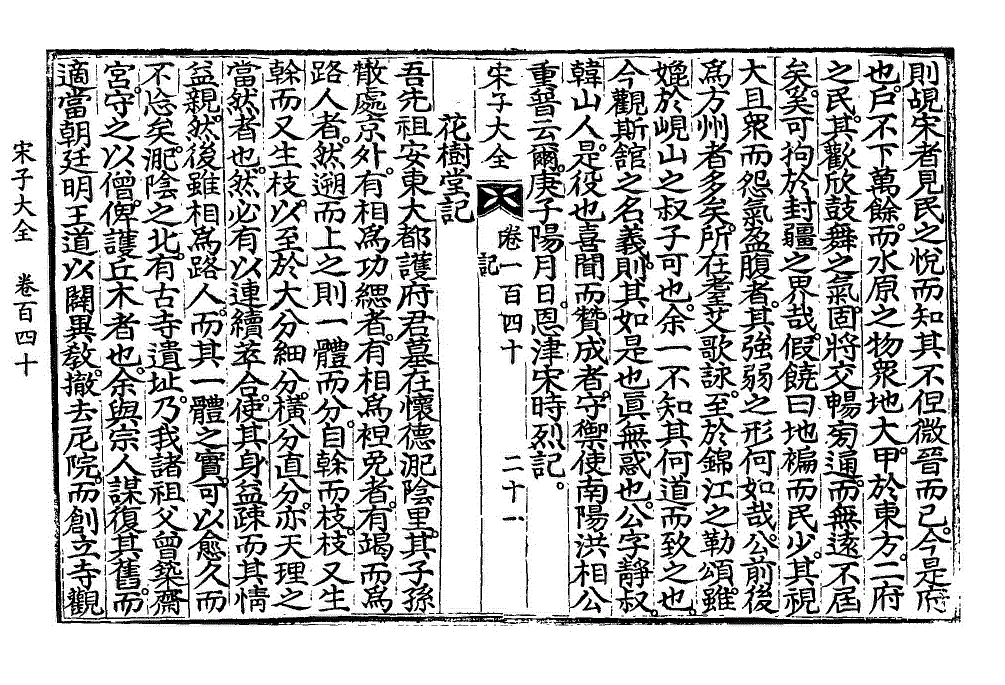 则觇宋者见民之悦而知其不但微晋而已。今是府也。户不下万馀。而水原之物众地大。甲于东方。二府之民。其欢欣鼓舞之气。固将交畅旁通。而无远不届矣。奚可拘于封疆之界哉。假饶曰地褊而民少。其视大且众而怨气盈腹者。其强弱之形何如哉。公前后为方州者多矣。所在耋艾歌咏。至于锦江之勒颂。虽媲于岘山之叔子可也。余一不知其何道而致之也。今观斯馆之名义。则其如是也真无惑也。公字静叔。韩山人。是役也喜闻而赞成者。守御使南阳洪相公重普云尔。庚子阳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则觇宋者见民之悦而知其不但微晋而已。今是府也。户不下万馀。而水原之物众地大。甲于东方。二府之民。其欢欣鼓舞之气。固将交畅旁通。而无远不届矣。奚可拘于封疆之界哉。假饶曰地褊而民少。其视大且众而怨气盈腹者。其强弱之形何如哉。公前后为方州者多矣。所在耋艾歌咏。至于锦江之勒颂。虽媲于岘山之叔子可也。余一不知其何道而致之也。今观斯馆之名义。则其如是也真无惑也。公字静叔。韩山人。是役也喜闻而赞成者。守御使南阳洪相公重普云尔。庚子阳月日。恩津宋时烈记。花树堂记
吾先祖安东大都护府君墓在怀德淝阴里。其子孙散处京外。有相为功缌者。有相为袒免者。有竭而为路人者。然溯而上之则一体而分。自干而枝。枝又生干而又生枝。以至于大分细分。横分直分。亦天理之当然者也。然必有以连续萃合。使其身益疏而其情益亲。然后虽相为路人。而其一体之实。可以愈久而不忘矣。淝阴之北。有古寺遗址。乃我诸祖父曾筑斋宫。守之以僧。俾护丘木者也。余与宗人谋复其旧。而适当朝廷明王道以辟异教。撤去尼院。而创立寺观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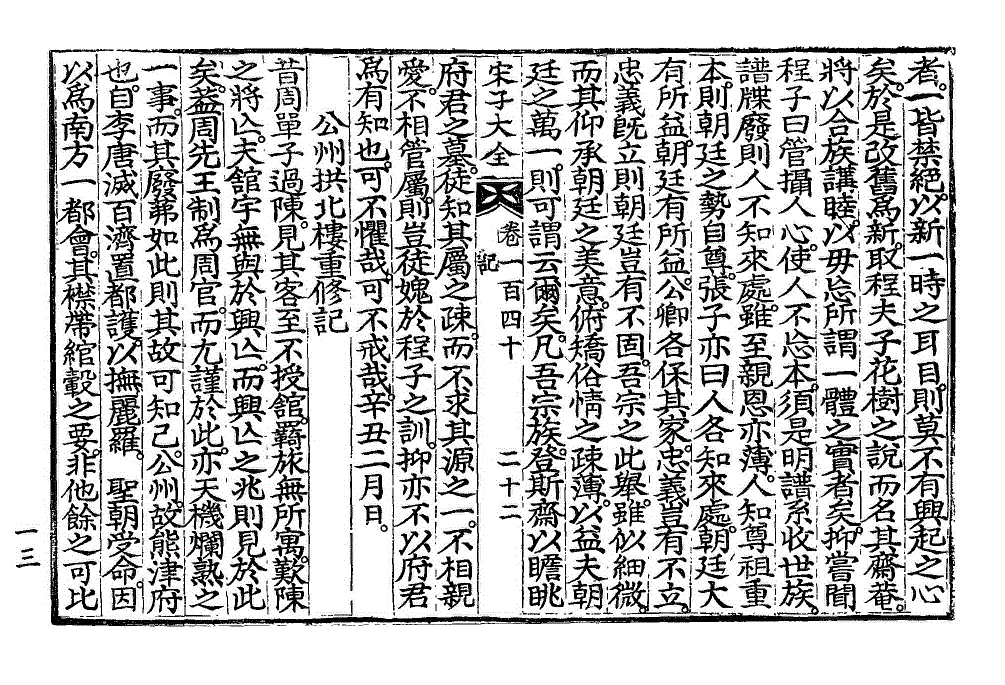 者。一皆禁绝。以新一时之耳目。则莫不有兴起之心矣。于是改旧为新。取程夫子花树之说而名其斋庵。将以合族讲睦。以毋忘所谓一体之实者矣。抑尝闻程子曰管摄人心。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谱牒废则人不知来处。虽至亲恩亦薄。人知尊祖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张子亦曰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朝廷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则朝廷岂有不固。吾宗之此举。虽似细微。而其仰承朝廷之美意。俯矫俗情之疏薄。以益夫朝廷之万一。则可谓云尔矣。凡吾宗族。登斯斋以瞻眺府君之墓。徒知其属之疏。而不求其源之一。不相亲爱。不相管属。则岂徒愧于程子之训。抑亦不以府君为有知也。可不惧哉。可不戒哉。辛丑二月日。
者。一皆禁绝。以新一时之耳目。则莫不有兴起之心矣。于是改旧为新。取程夫子花树之说而名其斋庵。将以合族讲睦。以毋忘所谓一体之实者矣。抑尝闻程子曰管摄人心。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谱牒废则人不知来处。虽至亲恩亦薄。人知尊祖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张子亦曰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朝廷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则朝廷岂有不固。吾宗之此举。虽似细微。而其仰承朝廷之美意。俯矫俗情之疏薄。以益夫朝廷之万一。则可谓云尔矣。凡吾宗族。登斯斋以瞻眺府君之墓。徒知其属之疏。而不求其源之一。不相亲爱。不相管属。则岂徒愧于程子之训。抑亦不以府君为有知也。可不惧哉。可不戒哉。辛丑二月日。公州拱北楼重修记
昔周单子过陈。见其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叹陈之将亡。夫馆宇无与于兴亡。而兴亡之兆则见于此矣。盖周先王制为周官。而尤谨于此。亦天机烂熟之一事。而其废茀如此则其故可知已。公州。故熊津府也。自李唐灭百济置都护。以抚丽罗。 圣朝受命。因以为南方一都会。其襟带绾毂之要。非他馀之可比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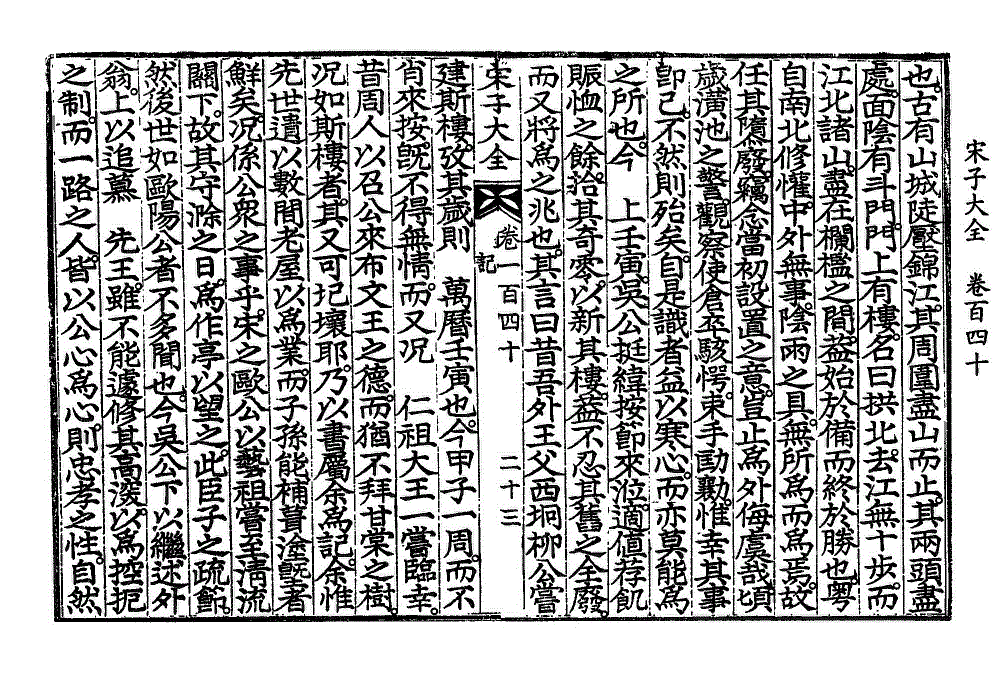 也。古有山城陡压锦江。其周围尽山而止。其两头尽处。面阴有斗门。门上有楼。名曰拱北。去江无十步。而江北诸山。尽在栏槛之间。盖始于备而终于胜也。粤自南北修欢。中外无事。阴雨之具。无所为而为焉。故任其隳废。窃念当初设置之意。岂止为外侮虞哉。顷岁潢池之警。观察使仓卒骇愕。束手劻勷。惟幸其事即已。不然则殆矣。自是识者益以寒心。而亦莫能为之所也。今 上壬寅。吴公挺纬按节来涖。适值荐饥赈恤之馀。拾其奇零。以新其楼。盖不忍其旧之全废。而又将为之兆也。其言曰昔吾外王父西坰柳公尝建斯楼。考其岁则 万历壬寅也。今甲子一周。而不肖来按。既不得无情。而又况 仁祖大王一尝临幸。昔周人以召公来布文王之德。而犹不拜甘棠之树。况如斯楼者。其又可圮坏耶。乃以书属余为记。余惟先世遗以数间老屋以为业。而子孙能补葺涂塈者鲜矣。况系公众之事乎。宋之欧公以艺祖尝至清流关下。故其守滁之日。为作亭以望之。此臣子之疏节。然后世如欧阳公者不多闻也。今吴公下以继述外翁。上以追慕 先王。虽不能遽修其高深。以为控扼之制。而一路之人。皆以公心为心。则忠孝之性。自然
也。古有山城陡压锦江。其周围尽山而止。其两头尽处。面阴有斗门。门上有楼。名曰拱北。去江无十步。而江北诸山。尽在栏槛之间。盖始于备而终于胜也。粤自南北修欢。中外无事。阴雨之具。无所为而为焉。故任其隳废。窃念当初设置之意。岂止为外侮虞哉。顷岁潢池之警。观察使仓卒骇愕。束手劻勷。惟幸其事即已。不然则殆矣。自是识者益以寒心。而亦莫能为之所也。今 上壬寅。吴公挺纬按节来涖。适值荐饥赈恤之馀。拾其奇零。以新其楼。盖不忍其旧之全废。而又将为之兆也。其言曰昔吾外王父西坰柳公尝建斯楼。考其岁则 万历壬寅也。今甲子一周。而不肖来按。既不得无情。而又况 仁祖大王一尝临幸。昔周人以召公来布文王之德。而犹不拜甘棠之树。况如斯楼者。其又可圮坏耶。乃以书属余为记。余惟先世遗以数间老屋以为业。而子孙能补葺涂塈者鲜矣。况系公众之事乎。宋之欧公以艺祖尝至清流关下。故其守滁之日。为作亭以望之。此臣子之疏节。然后世如欧阳公者不多闻也。今吴公下以继述外翁。上以追慕 先王。虽不能遽修其高深。以为控扼之制。而一路之人。皆以公心为心。则忠孝之性。自然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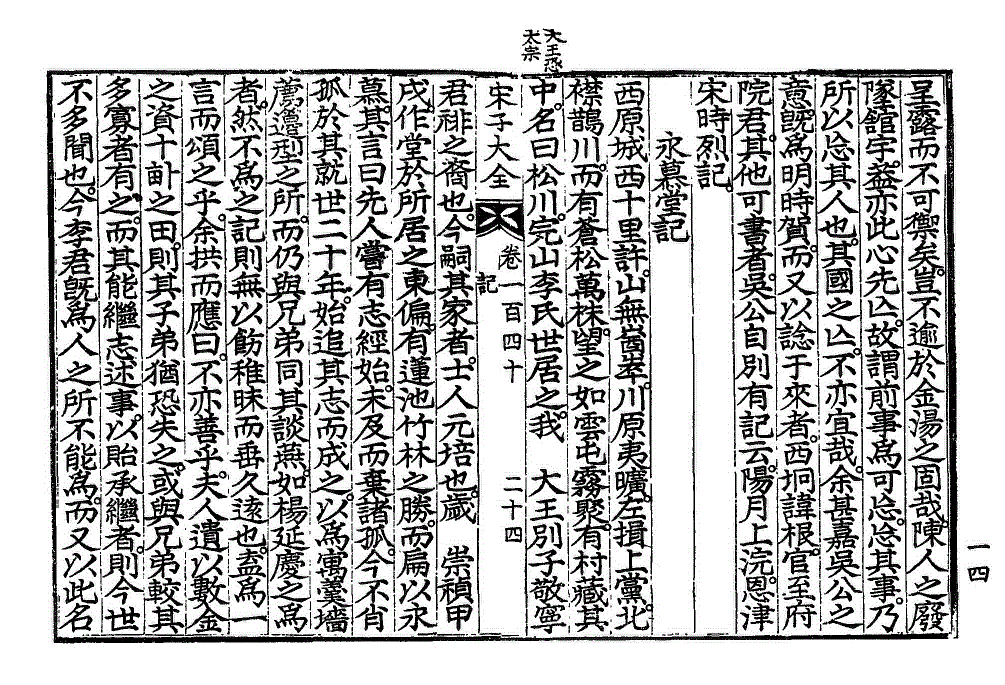 呈露而不可御矣。岂不逾于金汤之固哉。陈人之废坠馆宇。盖亦此心先亡。故谓前事为可忘。忘其事。乃所以忘其人也。其国之亡。不亦宜哉。余甚嘉吴公之意。既为明时贺。而又以谂于来者。西坰讳根。官至府院君。其他可书者。吴公自别有记云。阳月上浣。恩津宋时烈记。
呈露而不可御矣。岂不逾于金汤之固哉。陈人之废坠馆宇。盖亦此心先亡。故谓前事为可忘。忘其事。乃所以忘其人也。其国之亡。不亦宜哉。余甚嘉吴公之意。既为明时贺。而又以谂于来者。西坰讳根。官至府院君。其他可书者。吴公自别有记云。阳月上浣。恩津宋时烈记。永慕堂记
西原城西十里许。山无崷崒。川原夷旷。左揖上党。北襟鹊川。而有苍松万株。望之如云屯雾聚。有村藏其中。名曰松川。完山李氏世居之。我 大王(大王恐太宗)别子敬宁君𰨅之裔也。今嗣其家者。士人元培也。岁 崇祯甲戌。作堂于所居之东偏。有莲池竹林之胜。而扁以永慕。其言曰先人尝有志经始。未及而弃诸孤。今不肖孤于其就世二十年。始追其志而成之。以为寓羹墙荐笾型之所。而仍与兄弟同其谈燕。如杨延庆之为者。然不为之记则无以饬稚昧而垂久远也。盍为一言而颂之乎。余拱而应曰。不亦善乎。夫人遗以数金之资十亩之田。则其子弟犹恐失之。或与兄弟较其多寡者有之。而其能继志述事。以贻承继者。则今世不多闻也。今李君既为人之所不能为。而又以此名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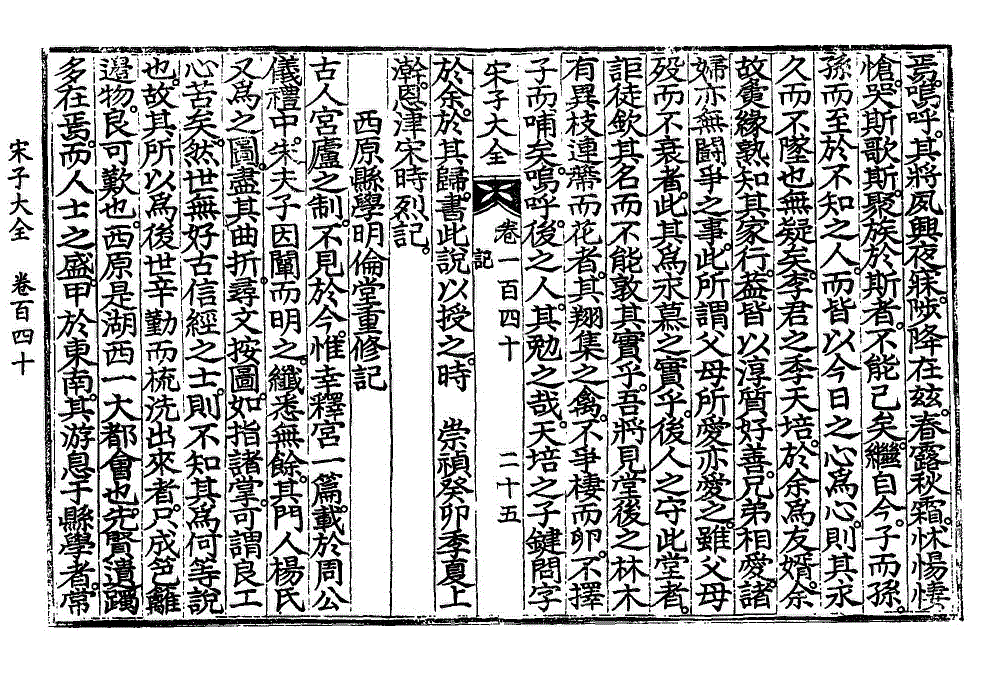 焉。呜呼。其将夙兴夜寐。陟降在玆。春露秋霜。怵惕悽怆。哭斯歌斯。聚族于斯者。不能已矣。继自今。子而孙。孙而至于不知之人。而皆以今日之心为心。则其永久而不坠也无疑矣。李君之季天培。于余为友婿。余故夤缘熟知其家行。盖皆以淳质好善。兄弟相爱。诸妇亦无斗争之事。此所谓父母所爱亦爱之。虽父母殁而不衰者。此其为永慕之实乎。后人之守此堂者。讵徒钦其名而不能敦其实乎。吾将见堂后之林木有异枝连蒂而花者。其翔集之禽。不争栖而卵。不择子而哺矣。呜呼。后之人。其勉之哉。天培之子键问字于余。于其归。书此说以授之。时 崇祯癸卯季夏上浣。恩津宋时烈记。
焉。呜呼。其将夙兴夜寐。陟降在玆。春露秋霜。怵惕悽怆。哭斯歌斯。聚族于斯者。不能已矣。继自今。子而孙。孙而至于不知之人。而皆以今日之心为心。则其永久而不坠也无疑矣。李君之季天培。于余为友婿。余故夤缘熟知其家行。盖皆以淳质好善。兄弟相爱。诸妇亦无斗争之事。此所谓父母所爱亦爱之。虽父母殁而不衰者。此其为永慕之实乎。后人之守此堂者。讵徒钦其名而不能敦其实乎。吾将见堂后之林木有异枝连蒂而花者。其翔集之禽。不争栖而卵。不择子而哺矣。呜呼。后之人。其勉之哉。天培之子键问字于余。于其归。书此说以授之。时 崇祯癸卯季夏上浣。恩津宋时烈记。西原县学明伦堂重修记
古人宫庐之制。不见于今。惟幸释宫一篇。载于周公仪礼中。朱夫子因阐而明之。纤悉无馀。其门人杨氏又为之图。尽其曲折。寻文按图。如指诸掌。可谓良工心苦矣。然世无好古信经之士。则不知其为何等说也。故其所以为后世辛勤而梳洗出来者。只成笆篱边物。良可叹也。西原是湖西一大都会也。先贤遗躅多在焉。而人士之盛。甲于东南。其游息于县学者。常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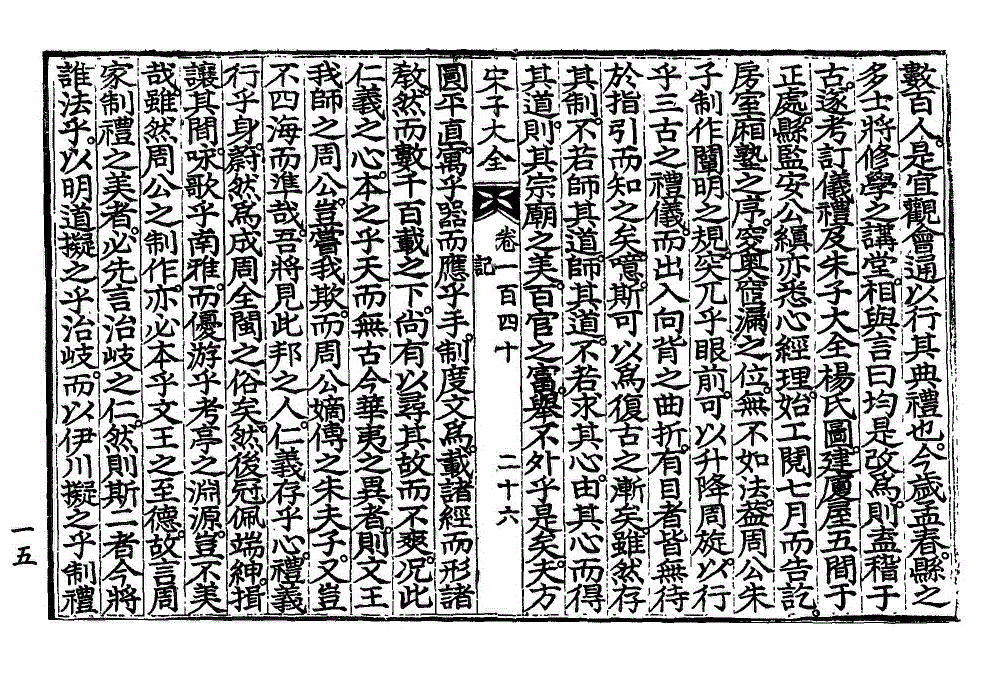 数百人。是宜观会通以行其典礼也。今岁孟春。县之多士将修学之讲堂。相与言曰均是改为。则盍稽于古。遂考订仪礼及朱子大全杨氏图。建厦屋五间于正处。县监安公缜亦悉心经理。始工阅七月而告讫。房室厢塾之序。窔奥宦漏之位。无不如法。盖周公,朱子制作阐明之规。突兀乎眼前。可以升降周旋。以行乎三古之礼仪。而出入向背之曲折。有目者皆无待于指引而知之矣。噫。斯可以为复古之渐矣。虽然存其制。不若师其道。师其道。不若求其心。由其心而得其道。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举不外乎是矣。夫方圆平直。寓乎器而应乎手。制度文为。载诸经而形诸教。然而数千百载之下。尚有以寻其故而不爽。况此仁义之心。本之乎天而无古今华夷之异者。则文王我师之周公。岂尝我欺。而周公嫡传之朱夫子。又岂不四海而准哉。吾将见此邦之人。仁义存乎心。礼义行乎身。蔚然为成周全闽之俗矣。然后冠佩端绅。揖让其间。咏歌乎南雅。而优游乎考亭之渊源。岂不美哉。虽然周公之制作。亦必本乎文王之至德。故言周家制礼之美者。必先言治岐之仁。然则斯二者今将谁法乎。以明道拟之乎治岐。而以伊川拟之乎制礼
数百人。是宜观会通以行其典礼也。今岁孟春。县之多士将修学之讲堂。相与言曰均是改为。则盍稽于古。遂考订仪礼及朱子大全杨氏图。建厦屋五间于正处。县监安公缜亦悉心经理。始工阅七月而告讫。房室厢塾之序。窔奥宦漏之位。无不如法。盖周公,朱子制作阐明之规。突兀乎眼前。可以升降周旋。以行乎三古之礼仪。而出入向背之曲折。有目者皆无待于指引而知之矣。噫。斯可以为复古之渐矣。虽然存其制。不若师其道。师其道。不若求其心。由其心而得其道。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举不外乎是矣。夫方圆平直。寓乎器而应乎手。制度文为。载诸经而形诸教。然而数千百载之下。尚有以寻其故而不爽。况此仁义之心。本之乎天而无古今华夷之异者。则文王我师之周公。岂尝我欺。而周公嫡传之朱夫子。又岂不四海而准哉。吾将见此邦之人。仁义存乎心。礼义行乎身。蔚然为成周全闽之俗矣。然后冠佩端绅。揖让其间。咏歌乎南雅。而优游乎考亭之渊源。岂不美哉。虽然周公之制作。亦必本乎文王之至德。故言周家制礼之美者。必先言治岐之仁。然则斯二者今将谁法乎。以明道拟之乎治岐。而以伊川拟之乎制礼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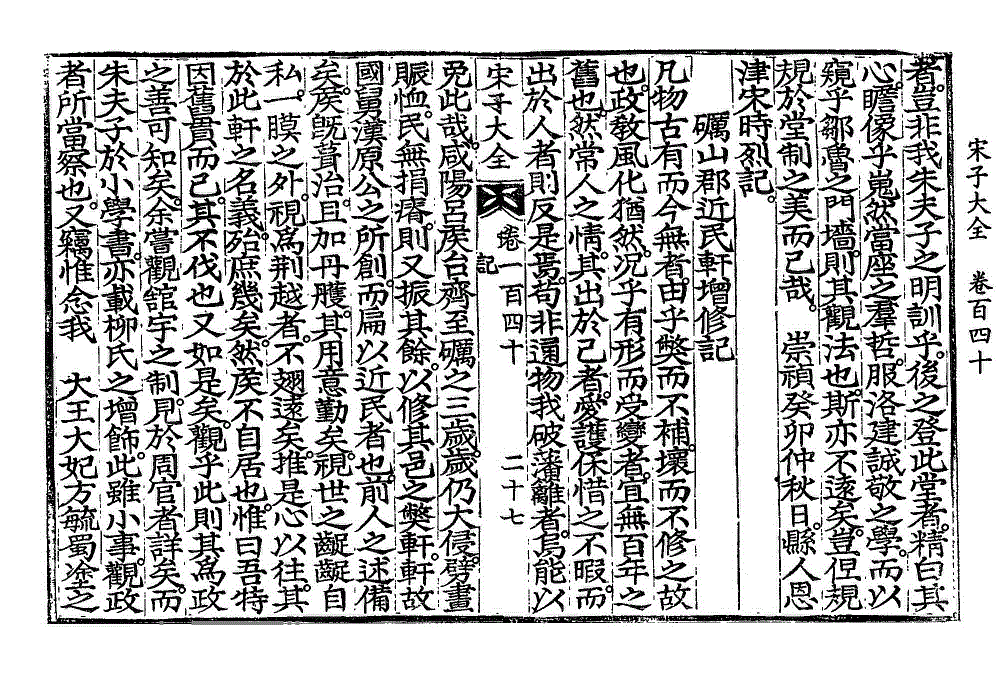 者。岂非我朱夫子之明训乎。后之登此堂者。精白其心。瞻像乎嵬然当座之群哲。服洛建诚敬之学。而以窥乎邹鲁之门墙。则其观法也。斯亦不远矣。岂但规规于堂制之美而已哉。 崇祯癸卯仲秋日。县人恩津宋时烈记。
者。岂非我朱夫子之明训乎。后之登此堂者。精白其心。瞻像乎嵬然当座之群哲。服洛建诚敬之学。而以窥乎邹鲁之门墙。则其观法也。斯亦不远矣。岂但规规于堂制之美而已哉。 崇祯癸卯仲秋日。县人恩津宋时烈记。砺山郡近民轩增修记
凡物古有而今无者。由乎弊而不补。坏而不修之故也。政教风化犹然。况乎有形而受变者。宜无百年之旧也。然常人之情。其出于己者。爱护保惜之不暇。而出于人者则反是焉。苟非通物我破藩篱者。乌能以免此哉。咸阳吕侯台齐至砺之三岁。岁仍大侵。劈画赈恤。民无捐瘠。则又振其馀。以修其邑之弊轩。轩故国舅汉原公之所创。而扁以近民者也。前人之述备矣。侯既葺治。且加丹雘。其用意勤矣。视世之龊龊自私。一膜之外。视为荆越者。不翅远矣。推是心以往。其于此轩之名义。殆庶几矣。然侯不自居也。惟曰吾特因旧贯而已。其不伐也又如是矣。观乎此则其为政之善可知矣。余尝观馆宇之制。见于周官者详矣。而朱夫子于小学书。亦载柳氏之增饰。此虽小事。观政者所当察也。又窃惟念我 大王大妃方毓蜀涂之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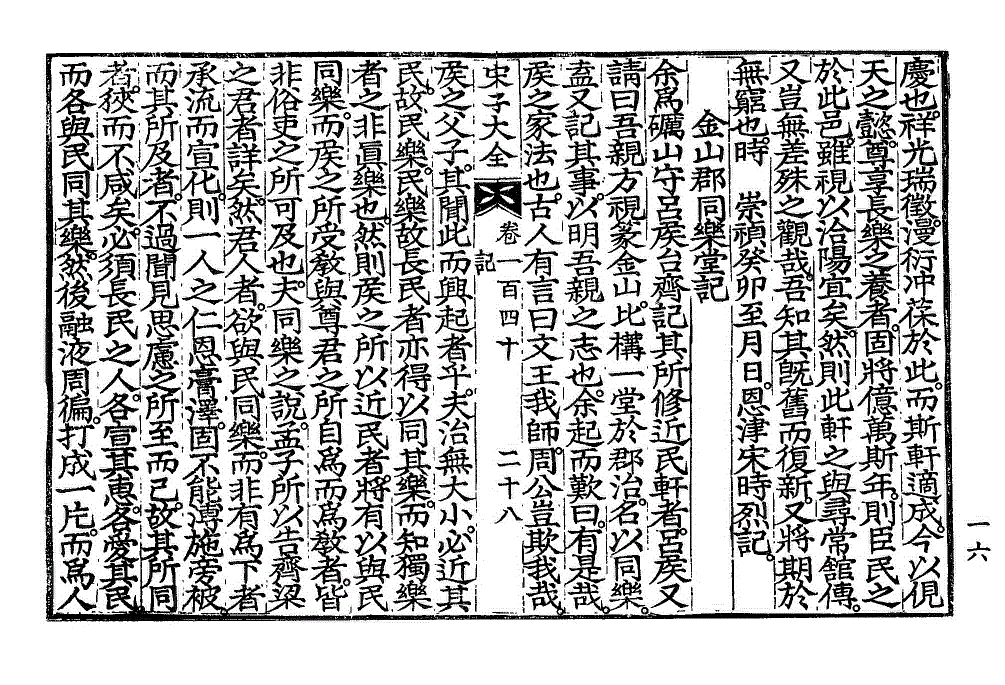 庆也。祥光瑞徵。漫衍冲葆于此。而斯轩适成。今以伣天之懿。尊享长乐之养者。固将亿万斯年。则臣民之于此邑。虽视以洽阳宜矣。然则此轩之与寻常馆传。又岂无差殊之观哉。吾知其既旧而复新。又将期于无穷也。时 崇祯癸卯至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庆也。祥光瑞徵。漫衍冲葆于此。而斯轩适成。今以伣天之懿。尊享长乐之养者。固将亿万斯年。则臣民之于此邑。虽视以洽阳宜矣。然则此轩之与寻常馆传。又岂无差殊之观哉。吾知其既旧而复新。又将期于无穷也。时 崇祯癸卯至月日。恩津宋时烈记。金山郡同乐堂记
余为砺山守吕侯台齐记其所修近民轩者。吕侯又请曰吾亲方视篆金山。比构一堂于郡治。名以同乐。盍又记其事。以明吾亲之志也。余起而叹曰。有是哉。侯之家法也。古人有言曰文王我师。周公岂欺我哉。侯之父子。其闻此而兴起者乎。夫治无大小。必近其民。故民乐。民乐故长民者亦得以同其乐。而知独乐者之非真乐也。然则侯之所以近民者。将有以与民同乐。而侯之所受教与尊君之所自为而为教者。皆非俗吏之所可及也。夫同乐之说。孟子所以告齐梁之君者详矣。然君人者。欲与民同乐。而非有为下者承流而宣化。则一人之仁恩膏泽。固不能溥施旁被。而其所及者。不过闻见思虑之所至而已。故其所同者。狭而不咸矣。必须长民之人。各宣其惠。各爱其民。而各与民同其乐。然后融液周遍。打成一片。而为人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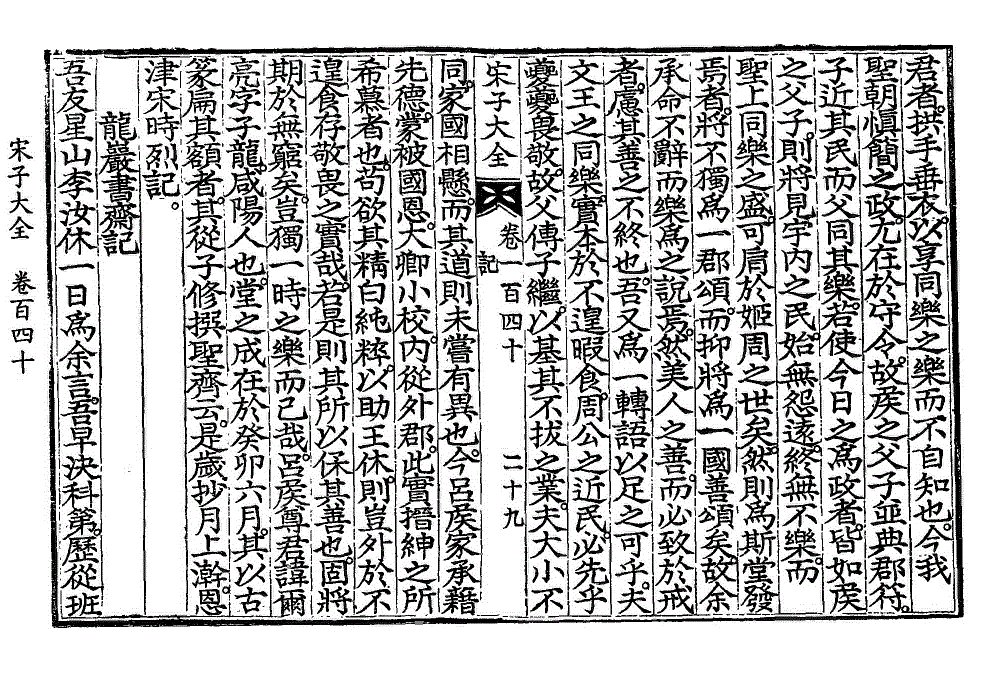 君者。拱手垂衣。以享同乐之乐而不自知也。今我 圣朝慎简之政。尤在于守令。故侯之父子并典郡符。子近其民而父同其乐。若使今日之为政者。皆如侯之父子。则将见宇内之民。始无怨远。终无不乐。而 圣上同乐之盛。可肩于姬周之世矣。然则为斯堂发焉者。将不独为一郡颂。而抑将为一国善颂矣。故余承命不辞而乐为之说焉。然美人之善。而必致于戒者。虑其善之不终也。吾又为一转语以足之可乎。夫文王之同乐。实本于不遑暇食。周公之近民。必先乎夔夔畏敬。故父传子继。以基其不拔之业。夫大小不同。家国相悬。而其道则未尝有异也。今吕侯家承藉先德。蒙被国恩。大卿小校。内从外郡。此实搢绅之所希慕者也。苟欲其精白纯粹。以助王休。则岂外于不遑食存敬畏之实哉。若是则其所以保其善也。固将期于无穷矣。岂独一时之乐而已哉。吕侯尊君讳尔亮字子龙。咸阳人也。堂之成在于癸卯六月。其以古篆扁其额者。其从子修撰圣齐云。是岁抄(一作杪)月上浣。恩津宋时烈记。
君者。拱手垂衣。以享同乐之乐而不自知也。今我 圣朝慎简之政。尤在于守令。故侯之父子并典郡符。子近其民而父同其乐。若使今日之为政者。皆如侯之父子。则将见宇内之民。始无怨远。终无不乐。而 圣上同乐之盛。可肩于姬周之世矣。然则为斯堂发焉者。将不独为一郡颂。而抑将为一国善颂矣。故余承命不辞而乐为之说焉。然美人之善。而必致于戒者。虑其善之不终也。吾又为一转语以足之可乎。夫文王之同乐。实本于不遑暇食。周公之近民。必先乎夔夔畏敬。故父传子继。以基其不拔之业。夫大小不同。家国相悬。而其道则未尝有异也。今吕侯家承藉先德。蒙被国恩。大卿小校。内从外郡。此实搢绅之所希慕者也。苟欲其精白纯粹。以助王休。则岂外于不遑食存敬畏之实哉。若是则其所以保其善也。固将期于无穷矣。岂独一时之乐而已哉。吕侯尊君讳尔亮字子龙。咸阳人也。堂之成在于癸卯六月。其以古篆扁其额者。其从子修撰圣齐云。是岁抄(一作杪)月上浣。恩津宋时烈记。龙岩书斋记
吾友星山李汝休一日为余言。吾早决科第。历从班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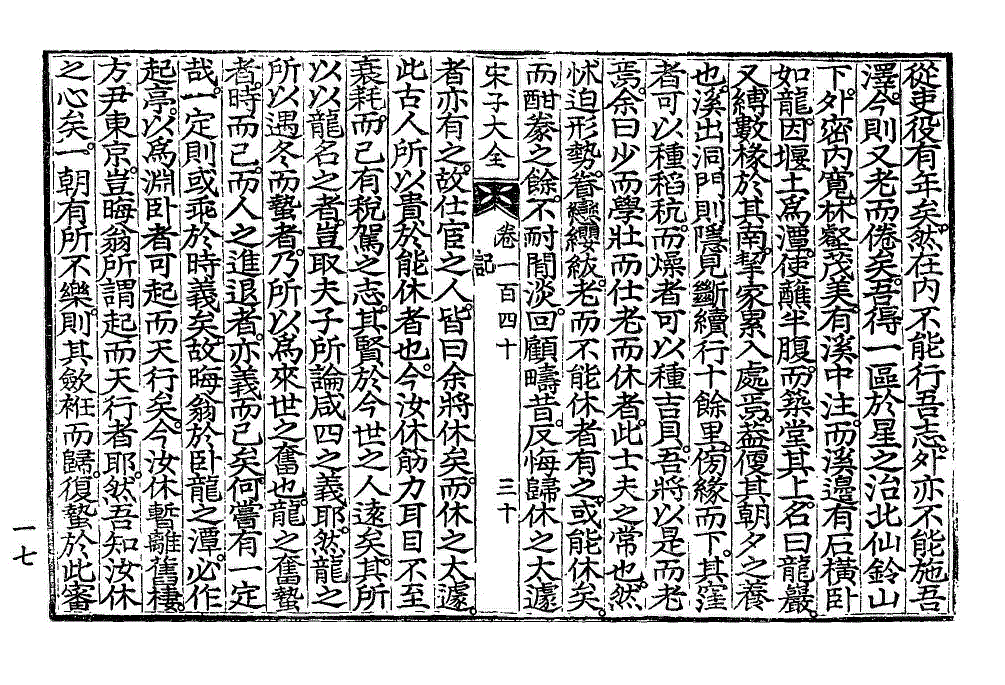 从吏役有年矣。然在内不能行吾志。外亦不能施吾泽。今则又老而倦矣。吾得一区于星之治北仙铃山下。外密内宽。林壑茂美。有溪中注。而溪边有石横卧如龙。因堰土为潭。使蘸半腹。而筑堂其上。名曰龙岩。又缚数椽于其南。挈家累入处焉。盖便其朝夕之养也。溪出洞门则隐见断续行十馀里。傍缘而下。其洼者可以种稻粳。而燥者可以种吉贝。吾将以是而老焉。余曰少而学壮而仕老而休者。此士夫之常也。然怵迫形势。眷恋缨绂。老而不能休者有之。或能休矣。而酣豢之馀。不耐閒淡。回顾畴昔。反悔归休之太遽者亦有之。故仕宦之人。皆曰余将休矣。而休之太遽。此古人所以贵于能休者也。今汝休筋力耳目不至衰耗。而已有税驾之志。其贤于今世之人远矣。其所以以龙名之者。岂取夫子所论咸四之义耶。然龙之所以遇冬而蛰者。乃所以为来世之奋也。龙之奋蛰者。时而已。而人之进退者。亦义而已矣。何尝有一定哉。一定则或乖于时义矣。故晦翁于卧龙之潭。必作起亭。以为渊卧者可起而天行矣。今汝休暂离旧栖。方尹东京。岂晦翁所谓起而天行者耶。然吾知汝休之心矣。一朝有所不乐。则其敛衽而归。复蛰于此审
从吏役有年矣。然在内不能行吾志。外亦不能施吾泽。今则又老而倦矣。吾得一区于星之治北仙铃山下。外密内宽。林壑茂美。有溪中注。而溪边有石横卧如龙。因堰土为潭。使蘸半腹。而筑堂其上。名曰龙岩。又缚数椽于其南。挈家累入处焉。盖便其朝夕之养也。溪出洞门则隐见断续行十馀里。傍缘而下。其洼者可以种稻粳。而燥者可以种吉贝。吾将以是而老焉。余曰少而学壮而仕老而休者。此士夫之常也。然怵迫形势。眷恋缨绂。老而不能休者有之。或能休矣。而酣豢之馀。不耐閒淡。回顾畴昔。反悔归休之太遽者亦有之。故仕宦之人。皆曰余将休矣。而休之太遽。此古人所以贵于能休者也。今汝休筋力耳目不至衰耗。而已有税驾之志。其贤于今世之人远矣。其所以以龙名之者。岂取夫子所论咸四之义耶。然龙之所以遇冬而蛰者。乃所以为来世之奋也。龙之奋蛰者。时而已。而人之进退者。亦义而已矣。何尝有一定哉。一定则或乖于时义矣。故晦翁于卧龙之潭。必作起亭。以为渊卧者可起而天行矣。今汝休暂离旧栖。方尹东京。岂晦翁所谓起而天行者耶。然吾知汝休之心矣。一朝有所不乐。则其敛衽而归。复蛰于此审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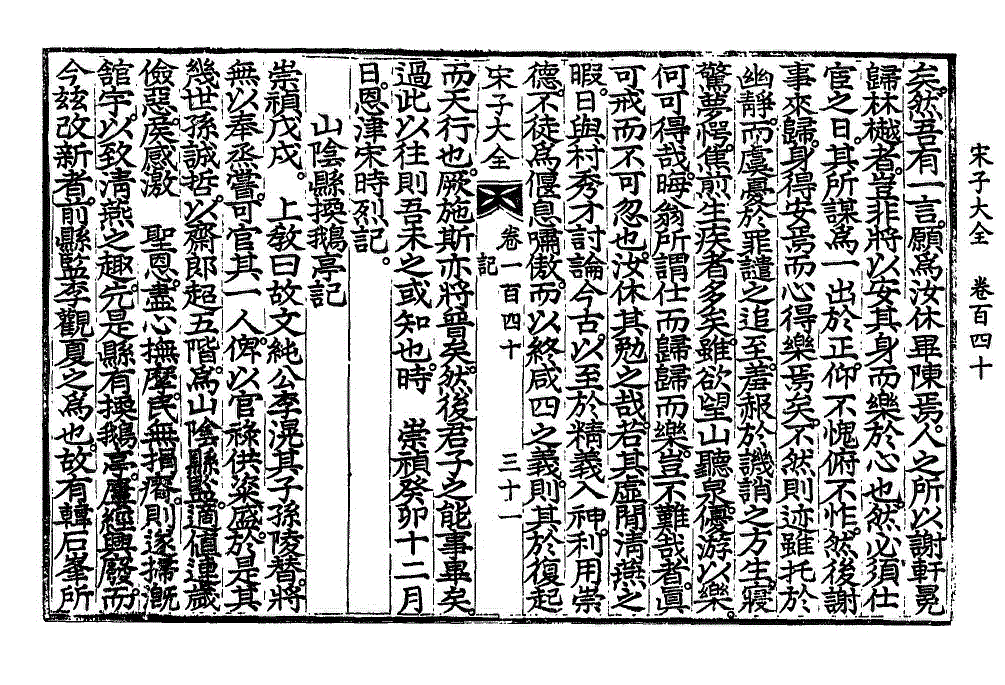 矣。然吾有一言。愿为汝休毕陈焉。人之所以谢轩冕归林樾者。岂非将以安其身而乐于心也。然必须仕宦之日。其所谋为一出于正。仰不愧俯不怍。然后谢事来归。身得安焉而心得乐焉矣。不然则迹虽托于幽静。而虞忧于罪谴之追至。羞赧于讥诮之方生。寝惊梦愕。焦煎生疾者多矣。虽欲望山听泉。优游以乐。何可得哉。晦翁所谓仕而归归而乐。岂不难哉者。真可戒而不可忽也。汝休其勉之哉。若其虚閒清燕之暇。日与村秀才讨论今古。以至于精义入神。利用崇德。不徒为偃息啸傲。而以终咸四之义。则其于复起而天行也。厥施斯亦将普矣。然后君子之能事毕矣。过此以往则吾未之或知也。时 崇祯癸卯十二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矣。然吾有一言。愿为汝休毕陈焉。人之所以谢轩冕归林樾者。岂非将以安其身而乐于心也。然必须仕宦之日。其所谋为一出于正。仰不愧俯不怍。然后谢事来归。身得安焉而心得乐焉矣。不然则迹虽托于幽静。而虞忧于罪谴之追至。羞赧于讥诮之方生。寝惊梦愕。焦煎生疾者多矣。虽欲望山听泉。优游以乐。何可得哉。晦翁所谓仕而归归而乐。岂不难哉者。真可戒而不可忽也。汝休其勉之哉。若其虚閒清燕之暇。日与村秀才讨论今古。以至于精义入神。利用崇德。不徒为偃息啸傲。而以终咸四之义。则其于复起而天行也。厥施斯亦将普矣。然后君子之能事毕矣。过此以往则吾未之或知也。时 崇祯癸卯十二月日。恩津宋时烈记。山阴县换鹅亭记
崇祯戊戌。 上教曰故文纯公李滉其子孙陵替。将无以奉烝尝。可官其一人。俾以官禄供粢盛。于是其几世孙诚哲。以斋郎超五阶。为山阴县监。适值连岁俭恶。侯感激 圣恩。尽心抚摩。民无捐瘠。则遂扫溉馆宇。以致清燕之趣。先是县有换鹅亭。屡经兴废。而今玆改新者。前县监李观夏之为也。故有韩石峰所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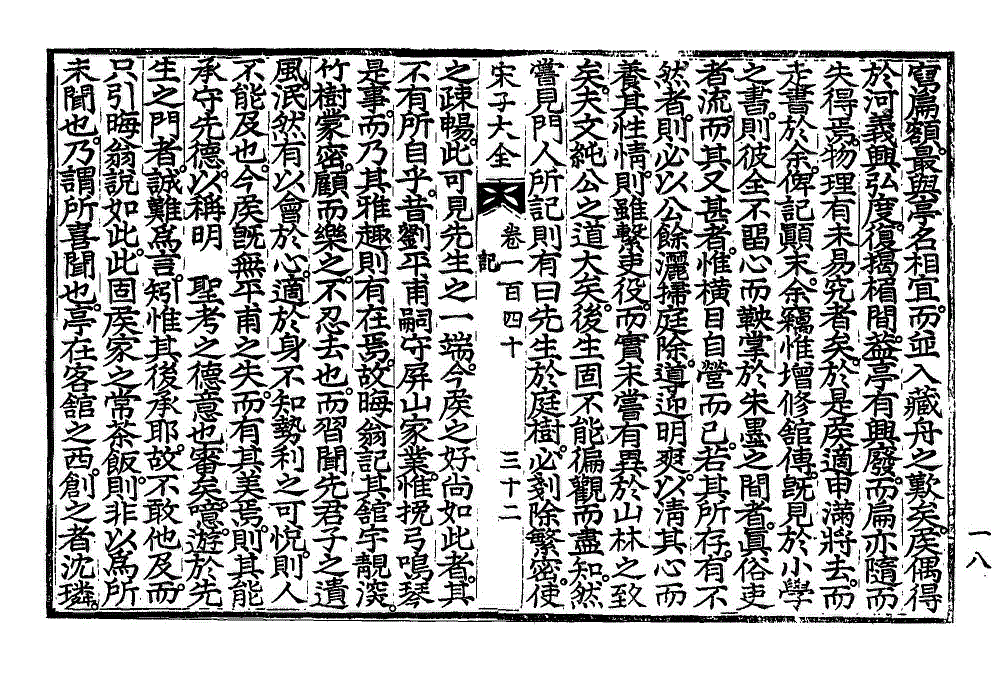 写扁额。最与亭名相宜。而并入藏舟之叹矣。侯偶得于河义兴弘度。复揭楣间。盖亭有兴废。而扁亦随而失得焉。物理有未易究者矣。于是侯适申满将去。而走书于余。俾记颠末。余窃惟增修馆传。既见于小学之书。则彼全不留心而鞅掌于朱墨之间者。真俗吏者流。而其又甚者。惟横目自营而已。若其所存。有不然者。则必以公馀洒扫庭除。导迎明爽。以清其心而养其性情。则虽系吏役。而实未尝有异于山林之致矣。夫文纯公之道大矣。后生固不能遍观而尽知。然尝见门人所记则有曰先生于庭树。必刬除繁密。使之疏畅。此可见先生之一端。今侯之好尚如此者。其不有所自乎。昔刘平甫嗣守屏山家业。惟挽弓鸣琴是事。而乃其雅趣则有在焉。故晦翁记其馆宇靓深。竹树蒙密。顾而乐之。不忍去也。而习闻先君子之遗风。泯然有以会于心。适于身不知势利之可悦。则人不能及也。今侯既无平甫之失。而有其美焉。则其能承守先德。以称明 圣考之德意也审矣。噫。游于先生之门者。诚难为言。矧惟其后承耶。故不敢他及。而只引晦翁说如此。此固侯家之常茶饭。则非以为所未闻也。乃谓所喜闻也。亭在客馆之西。创之者沈璘。
写扁额。最与亭名相宜。而并入藏舟之叹矣。侯偶得于河义兴弘度。复揭楣间。盖亭有兴废。而扁亦随而失得焉。物理有未易究者矣。于是侯适申满将去。而走书于余。俾记颠末。余窃惟增修馆传。既见于小学之书。则彼全不留心而鞅掌于朱墨之间者。真俗吏者流。而其又甚者。惟横目自营而已。若其所存。有不然者。则必以公馀洒扫庭除。导迎明爽。以清其心而养其性情。则虽系吏役。而实未尝有异于山林之致矣。夫文纯公之道大矣。后生固不能遍观而尽知。然尝见门人所记则有曰先生于庭树。必刬除繁密。使之疏畅。此可见先生之一端。今侯之好尚如此者。其不有所自乎。昔刘平甫嗣守屏山家业。惟挽弓鸣琴是事。而乃其雅趣则有在焉。故晦翁记其馆宇靓深。竹树蒙密。顾而乐之。不忍去也。而习闻先君子之遗风。泯然有以会于心。适于身不知势利之可悦。则人不能及也。今侯既无平甫之失。而有其美焉。则其能承守先德。以称明 圣考之德意也审矣。噫。游于先生之门者。诚难为言。矧惟其后承耶。故不敢他及。而只引晦翁说如此。此固侯家之常茶饭。则非以为所未闻也。乃谓所喜闻也。亭在客馆之西。创之者沈璘。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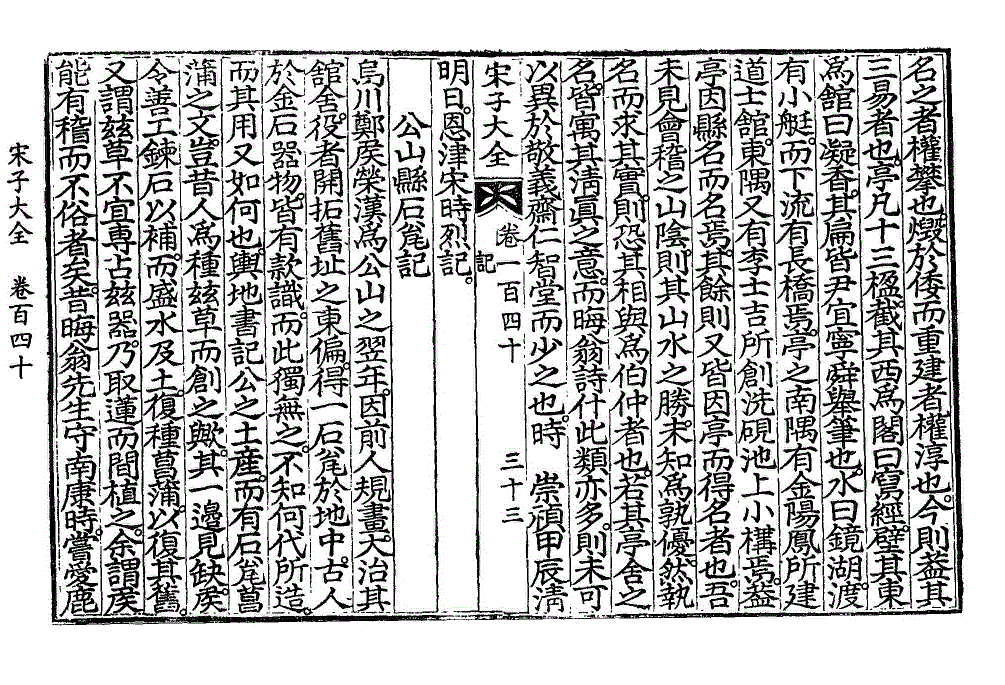 名之者权攀也。燬于倭而重建者权淳也。今则盖其三易者也。亭凡十三楹。截其西为阁曰写经。壁其东为馆曰凝香。其扁皆尹宜宁舜举笔也。水曰镜湖。渡有小艇。而下流有长桥焉。亭之南隅有金阳凤所建道士馆。东隅又有李士吉所创洗砚池上小构焉。盖亭因县名而名焉。其馀则又皆因亭而得名者也。吾未见会稽之山阴。则其山水之胜。未知为孰优。然执名而求其实。则恐其相与为伯仲者也。若其亭舍之名。皆寓其清真之意。而晦翁诗什此类亦多。则未可以异于敬义斋仁智堂而少之也。时 崇祯甲辰清明日。恩津宋时烈记。
名之者权攀也。燬于倭而重建者权淳也。今则盖其三易者也。亭凡十三楹。截其西为阁曰写经。壁其东为馆曰凝香。其扁皆尹宜宁舜举笔也。水曰镜湖。渡有小艇。而下流有长桥焉。亭之南隅有金阳凤所建道士馆。东隅又有李士吉所创洗砚池上小构焉。盖亭因县名而名焉。其馀则又皆因亭而得名者也。吾未见会稽之山阴。则其山水之胜。未知为孰优。然执名而求其实。则恐其相与为伯仲者也。若其亭舍之名。皆寓其清真之意。而晦翁诗什此类亦多。则未可以异于敬义斋仁智堂而少之也。时 崇祯甲辰清明日。恩津宋时烈记。公山县石瓮记
乌川郑侯荣汉为公山之翌年。因前人规画。大治其馆舍。役者开拓旧址之东偏。得一石瓮于地中。古人于金石器物。皆有款识。而此独无之。不知何代所造。而其用又如何也。舆地书记公之土产。而有石瓮菖蒲之文。岂昔人为种玆草而创之欤。其一边见缺。侯令善工鍊石以补。而盛水及土。复种菖蒲。以复其旧。又谓玆草不宜专占玆器。乃取莲而间植之。余谓侯能有稽而不俗者矣。昔晦翁先生守南康时。尝爱鹿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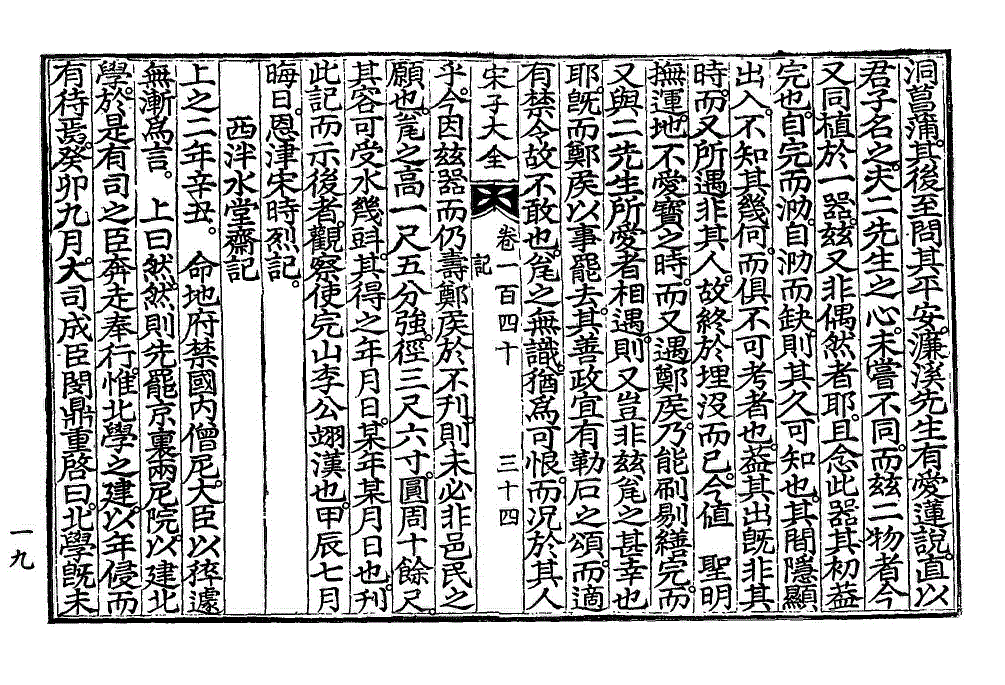 洞菖蒲。其后至问其平安。濂溪先生有爱莲说。直以君子名之。夫二先生之心。未尝不同。而玆二物者今又同植于一器。玆又非偶然者耶。且念此器其初盖完也。自完而泐。自泐而缺。则其久可知也。其间隐显出入。不知其几何。而俱不可考者也。盖其出既非其时。而又所遇非其人。故终于埋没而已。今值 圣明抚运。地不爱宝之时。而又遇郑侯。乃能刷剔缮完。而又与二先生所爱者相遇。则又岂非玆瓮之甚幸也耶。既而郑侯以事罢去。其善政宜有勒石之颂。而适有禁令故不敢也。瓮之无识。犹为可恨。而况于其人乎。今因玆器而仍寿郑侯于不刊。则未必非邑民之愿也。瓮之高一尺五分强。径三尺六寸。圆周十馀尺。其容可受水几斗。其得之年月日。某年某月日也。刊此记而示后者。观察使完山李公翊汉也。甲辰七月晦日。恩津宋时烈记。
洞菖蒲。其后至问其平安。濂溪先生有爱莲说。直以君子名之。夫二先生之心。未尝不同。而玆二物者今又同植于一器。玆又非偶然者耶。且念此器其初盖完也。自完而泐。自泐而缺。则其久可知也。其间隐显出入。不知其几何。而俱不可考者也。盖其出既非其时。而又所遇非其人。故终于埋没而已。今值 圣明抚运。地不爱宝之时。而又遇郑侯。乃能刷剔缮完。而又与二先生所爱者相遇。则又岂非玆瓮之甚幸也耶。既而郑侯以事罢去。其善政宜有勒石之颂。而适有禁令故不敢也。瓮之无识。犹为可恨。而况于其人乎。今因玆器而仍寿郑侯于不刊。则未必非邑民之愿也。瓮之高一尺五分强。径三尺六寸。圆周十馀尺。其容可受水几斗。其得之年月日。某年某月日也。刊此记而示后者。观察使完山李公翊汉也。甲辰七月晦日。恩津宋时烈记。西泮水堂斋记
上之二年辛丑。 命地府禁国内僧尼。大臣以猝遽无渐为言。 上曰然。然则先罢京里两尼院。以建北学。于是有司之臣奔走奉行。惟北学之建。以年侵而有待焉。癸卯九月。大司成臣闵鼎重启曰。北学既未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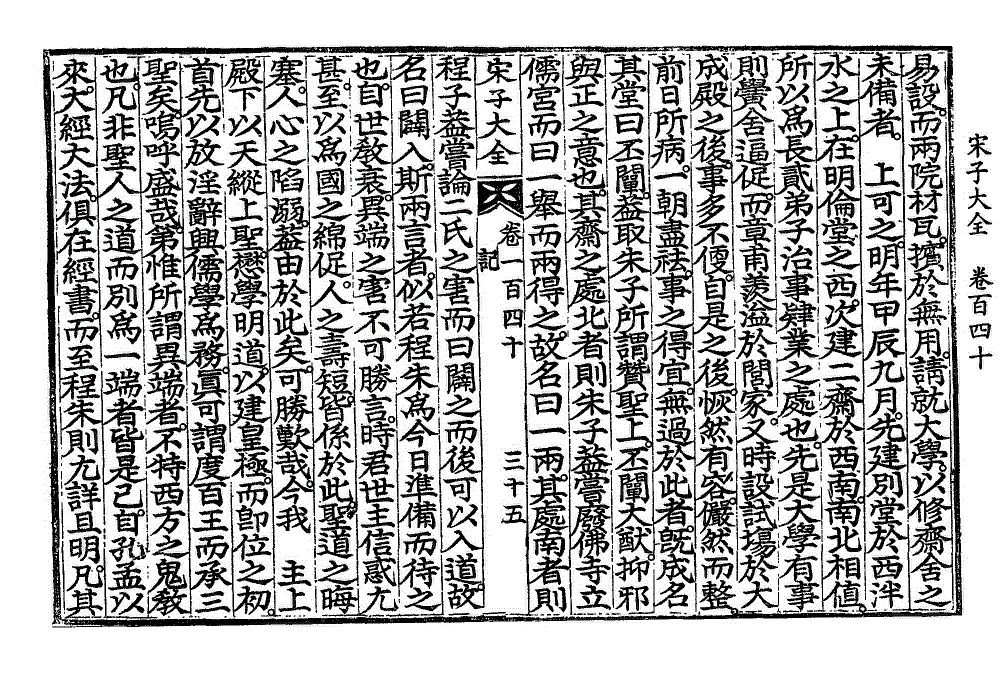 易设。而两院材瓦。摈于无用。请就大学。以修斋舍之未备者。 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建别堂于西泮水之上。在明伦堂之西。次建二斋于西南。南北相值。所以为长贰弟子治事肄业之处也。先是大学有事则黉舍逼促。而章甫羡溢于闾家。又时设试场于大成殿之后。事多不便。自是之后。恢然有容。俨然而整。前日所病。一朝尽祛。事之得宜。无过于此者。既成名其堂曰丕阐。盖取朱子所谓赞圣上。丕阐大猷。抑邪与正之意也。其斋之处北者则朱子盖尝废佛寺立儒宫而曰一举而两得之。故名曰一两。其处南者则程子盖尝论二氏之害而曰辟之而后可以入道。故名曰辟入。斯两言者。似若程朱为今日准备而待之也。自世教衰。异端之害不可胜言。时君世主信惑尤甚。至以为国之绵促。人之寿短。皆系于此。圣道之晦塞。人心之陷溺。盖由于此矣。可胜叹哉。今我 主上殿下以天纵上圣。懋学明道。以建皇极。而即位之初。首先以放淫辞兴儒学为务。真可谓度百王而承三圣矣。呜呼盛哉。第惟所谓异端者。不特西方之鬼教也。凡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皆是已。自孔孟以来。大经大法。俱在经书。而至程朱则尤详且明。凡其
易设。而两院材瓦。摈于无用。请就大学。以修斋舍之未备者。 上可之。明年甲辰九月。先建别堂于西泮水之上。在明伦堂之西。次建二斋于西南。南北相值。所以为长贰弟子治事肄业之处也。先是大学有事则黉舍逼促。而章甫羡溢于闾家。又时设试场于大成殿之后。事多不便。自是之后。恢然有容。俨然而整。前日所病。一朝尽祛。事之得宜。无过于此者。既成名其堂曰丕阐。盖取朱子所谓赞圣上。丕阐大猷。抑邪与正之意也。其斋之处北者则朱子盖尝废佛寺立儒宫而曰一举而两得之。故名曰一两。其处南者则程子盖尝论二氏之害而曰辟之而后可以入道。故名曰辟入。斯两言者。似若程朱为今日准备而待之也。自世教衰。异端之害不可胜言。时君世主信惑尤甚。至以为国之绵促。人之寿短。皆系于此。圣道之晦塞。人心之陷溺。盖由于此矣。可胜叹哉。今我 主上殿下以天纵上圣。懋学明道。以建皇极。而即位之初。首先以放淫辞兴儒学为务。真可谓度百王而承三圣矣。呜呼盛哉。第惟所谓异端者。不特西方之鬼教也。凡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皆是已。自孔孟以来。大经大法。俱在经书。而至程朱则尤详且明。凡其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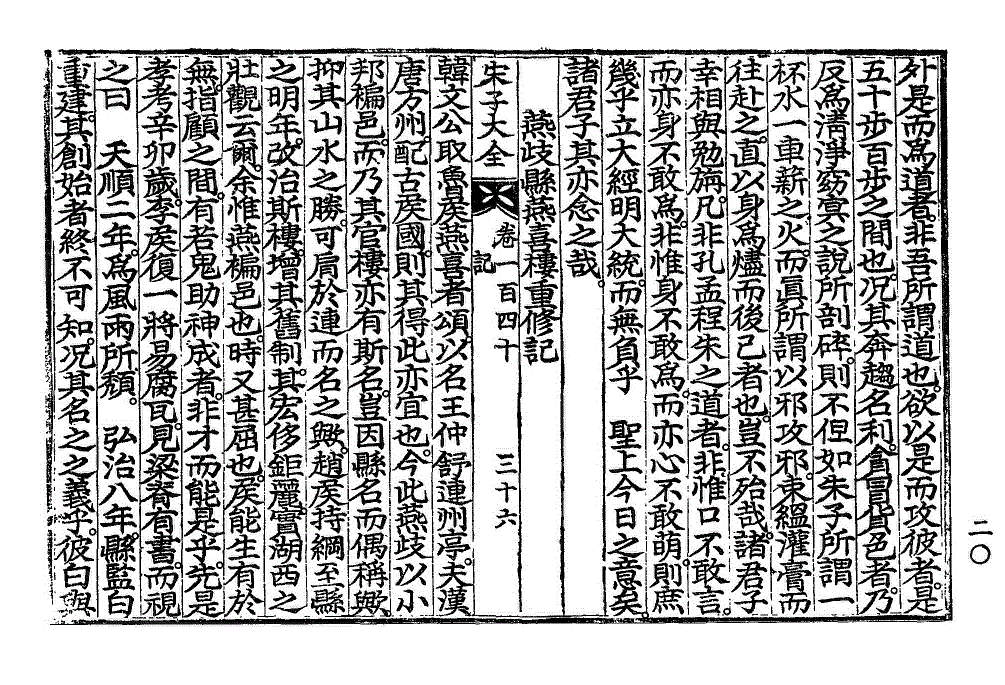 外是而为道者。非吾所谓道也。欲以是而攻彼者。是五十步百步之间也。况其奔趋名利。贪冒货色者。乃反为清净窈冥之说所剖碎。则不但如朱子所谓一杯水一车薪之火。而真所谓以邪攻邪。束缊灌膏而往赴之。直以身为烬而后已者也。岂不殆哉。诸君子幸相与勉旃。凡非孔孟程朱之道者。非惟口不敢言。而亦身不敢为。非惟身不敢为。而亦心不敢萌。则庶几乎立大经明大统。而无负乎 圣上今日之意矣。诸君子其亦念之哉。
外是而为道者。非吾所谓道也。欲以是而攻彼者。是五十步百步之间也。况其奔趋名利。贪冒货色者。乃反为清净窈冥之说所剖碎。则不但如朱子所谓一杯水一车薪之火。而真所谓以邪攻邪。束缊灌膏而往赴之。直以身为烬而后已者也。岂不殆哉。诸君子幸相与勉旃。凡非孔孟程朱之道者。非惟口不敢言。而亦身不敢为。非惟身不敢为。而亦心不敢萌。则庶几乎立大经明大统。而无负乎 圣上今日之意矣。诸君子其亦念之哉。燕岐县燕喜楼重修记
韩文公取鲁侯燕喜者颂。以名王仲舒连州亭。夫汉唐方州。配古侯国。则其得此亦宜也。今此燕岐以小邦褊邑。而乃其官楼亦有斯名。岂因县名而偶称欤。抑其山水之胜。可肩于连而名之欤。赵侯持纲至县之明年。改治斯楼。增其旧制。其宏侈钜丽。实湖西之壮观云尔。余惟燕褊邑也。时又甚屈也。侯能生有于无。指顾之间。有若鬼助神成者。非才而能是乎。先是孝考辛卯岁。李侯复一将易腐瓦。见梁脊有书。而视之曰 天顺二年。为风雨所颓。 弘治八年。县监白重建。其创始者终不可知。况其名之之义乎。彼白与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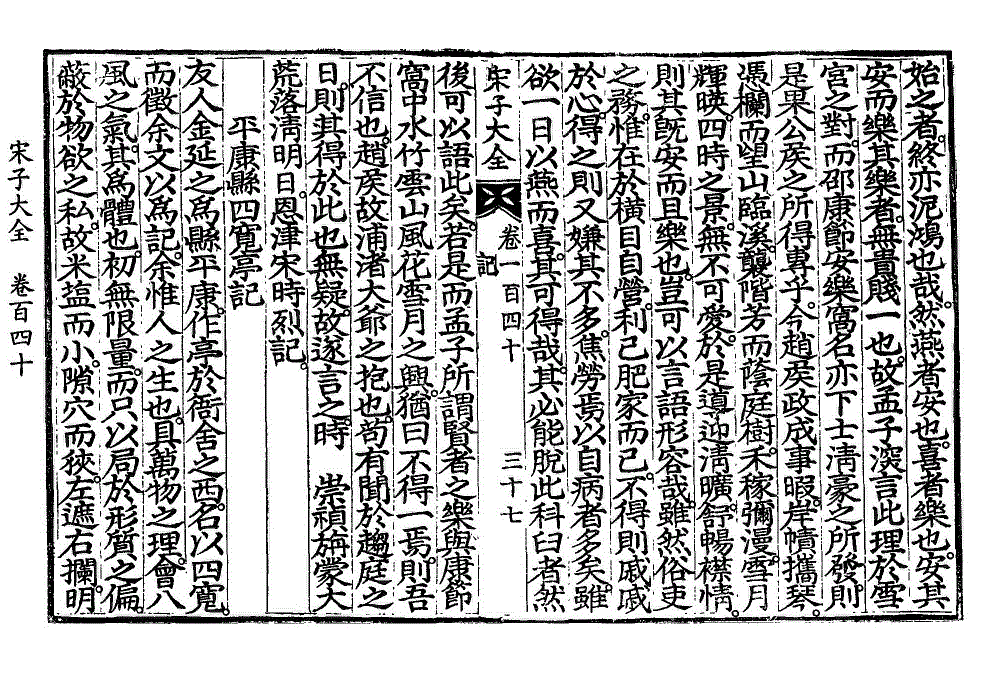 始之者。终亦泥鸿也哉。然燕者安也。喜者乐也。安其安而乐其乐者。无贵贱一也。故孟子深言此理于雪宫之对。而邵康节安乐窝名亦下士清豪之所发。则是果公侯之所得专乎。今赵侯政成事暇。岸帻携琴。凭栏而望山临溪。袭阶芳而荫庭树。禾稼弥漫。雪月辉映。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于是导迎清旷。舒畅襟情。则其既安而且乐也。岂可以言语形容哉。虽然俗吏之务。惟在于横目自营。利己肥家而已。不得则戚戚于心。得之则又嫌其不多。焦劳焉以自病者多矣。虽欲一日以燕而喜。其可得哉。其必能脱此科臼者然后可以语此矣。若是而孟子所谓贤者之乐与康节窝中水竹云山风花雪月之兴。犹曰不得一焉。则吾不信也。赵侯故浦渚大爷之抱也。苟有闻于趋庭之日。则其得于此也无疑。故遂言之。时 崇祯旃蒙大荒落清明日。恩津宋时烈记。
始之者。终亦泥鸿也哉。然燕者安也。喜者乐也。安其安而乐其乐者。无贵贱一也。故孟子深言此理于雪宫之对。而邵康节安乐窝名亦下士清豪之所发。则是果公侯之所得专乎。今赵侯政成事暇。岸帻携琴。凭栏而望山临溪。袭阶芳而荫庭树。禾稼弥漫。雪月辉映。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于是导迎清旷。舒畅襟情。则其既安而且乐也。岂可以言语形容哉。虽然俗吏之务。惟在于横目自营。利己肥家而已。不得则戚戚于心。得之则又嫌其不多。焦劳焉以自病者多矣。虽欲一日以燕而喜。其可得哉。其必能脱此科臼者然后可以语此矣。若是而孟子所谓贤者之乐与康节窝中水竹云山风花雪月之兴。犹曰不得一焉。则吾不信也。赵侯故浦渚大爷之抱也。苟有闻于趋庭之日。则其得于此也无疑。故遂言之。时 崇祯旃蒙大荒落清明日。恩津宋时烈记。平康县四宽亭记
友人金延之为县平康。作亭于衙舍之西。名以四宽。而徵余文以为记。余惟人之生也。具万物之理。会八风之气。其为体也。初无限量。而只以局于形质之偏。蔽于物欲之私。故米盐而小。隙穴而狭。左遮右拦。明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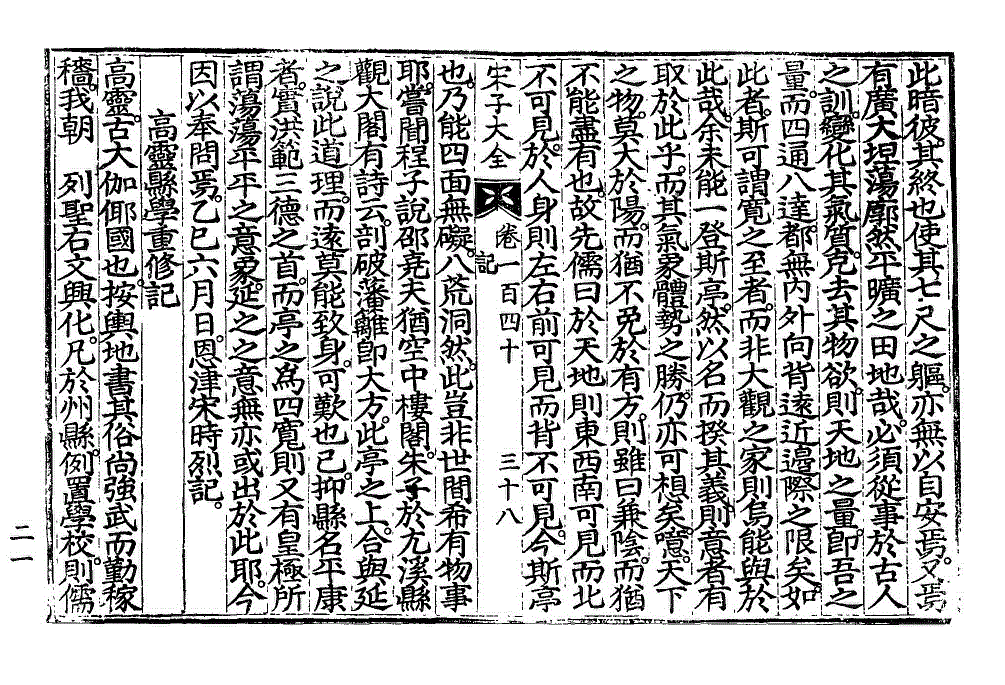 此暗彼。其终也使其七尺之躯。亦无以自安焉。又焉有广大坦荡廓然平旷之田地哉。必须从事于古人之训。变化其气质。克去其物欲。则天地之量。即吾之量。而四通八达。都无内外向背远近边际之限矣。如此者。斯可谓宽之至者。而非大观之家则乌能与于此哉。余未能一登斯亭。然以名而揆其义。则意者有取于此乎。而其气象体势之胜。仍亦可想矣。噫。天下之物。莫大于阳。而犹不免于有方。则虽曰兼阴。而犹不能尽有也。故先儒曰于天地则东西南可见而北不可见。于人身则左右前可见而背不可见。今斯亭也。乃能四面无碍。八荒洞然。此岂非世间希有物事耶。尝闻程子说邵尧夫犹空中楼阁。朱子于尤溪县观大阁有诗云。剖破藩篱即大方。此亭之上。合与延之说此道理。而远莫能致身。可叹也已。抑县名平康者。实洪范三德之首。而亭之为四宽则又有皇极所谓荡荡平平之意象。延之之意无亦或出于此耶。今因以奉问焉。乙巳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此暗彼。其终也使其七尺之躯。亦无以自安焉。又焉有广大坦荡廓然平旷之田地哉。必须从事于古人之训。变化其气质。克去其物欲。则天地之量。即吾之量。而四通八达。都无内外向背远近边际之限矣。如此者。斯可谓宽之至者。而非大观之家则乌能与于此哉。余未能一登斯亭。然以名而揆其义。则意者有取于此乎。而其气象体势之胜。仍亦可想矣。噫。天下之物。莫大于阳。而犹不免于有方。则虽曰兼阴。而犹不能尽有也。故先儒曰于天地则东西南可见而北不可见。于人身则左右前可见而背不可见。今斯亭也。乃能四面无碍。八荒洞然。此岂非世间希有物事耶。尝闻程子说邵尧夫犹空中楼阁。朱子于尤溪县观大阁有诗云。剖破藩篱即大方。此亭之上。合与延之说此道理。而远莫能致身。可叹也已。抑县名平康者。实洪范三德之首。而亭之为四宽则又有皇极所谓荡荡平平之意象。延之之意无亦或出于此耶。今因以奉问焉。乙巳六月日。恩津宋时烈记。高灵县学重修记
高灵。古大伽倻国也。按舆地书其俗尚强武而勤稼穑。我朝 列圣右文兴化。凡于州县。例置学校。则儒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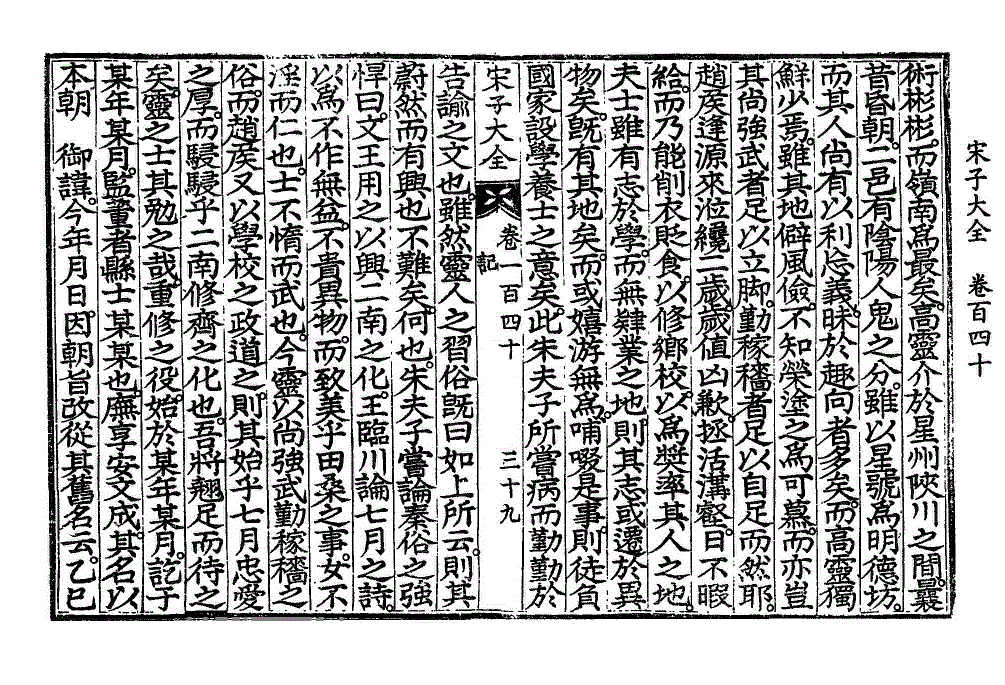 术彬彬。而岭南为最矣。高灵介于星州陜川之间。曩昔昏朝。二邑有阴阳人鬼之分。虽以星号为明德坊。而其人尚有以利忘义。昧于趣向者多矣。而高灵独鲜少焉。虽其地僻风俭。不知荣涂之为可慕。而亦岂其尚强武者足以立脚。勤稼穑者足以自足而然耶。赵侯逢源来涖才二岁。岁值凶歉。拯活沟壑。日不暇给。而乃能削衣贬食。以修乡校。以为奖率其人之地。夫士虽有志于学。而无肄业之地。则其志或迁于异物矣。既有其地矣。而或嬉游无为。哺啜是事。则徒负国家设学养士之意矣。此朱夫子所尝病而勤勤于告谕之文也。虽然灵人之习俗既曰如上所云。则其蔚然而有兴也不难矣。何也。朱夫子尝论秦俗之强悍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王临川论七月之诗。以为不作无益。不贵异物。而致美乎田桑之事。女不淫而仁也。士不惰而武也。今灵以尚强武勤稼穑之俗。而赵侯又以学校之政道之。则其始乎七月忠爱之厚。而骎骎乎二南修齐之化也。吾将翘足而待之矣。灵之士其勉之哉。重修之役。始于某年某月。讫于某年某月。监董者县士某某也。庑享安文成。其名以本朝 御讳。今年月日。因朝旨改从其旧名云。乙巳
术彬彬。而岭南为最矣。高灵介于星州陜川之间。曩昔昏朝。二邑有阴阳人鬼之分。虽以星号为明德坊。而其人尚有以利忘义。昧于趣向者多矣。而高灵独鲜少焉。虽其地僻风俭。不知荣涂之为可慕。而亦岂其尚强武者足以立脚。勤稼穑者足以自足而然耶。赵侯逢源来涖才二岁。岁值凶歉。拯活沟壑。日不暇给。而乃能削衣贬食。以修乡校。以为奖率其人之地。夫士虽有志于学。而无肄业之地。则其志或迁于异物矣。既有其地矣。而或嬉游无为。哺啜是事。则徒负国家设学养士之意矣。此朱夫子所尝病而勤勤于告谕之文也。虽然灵人之习俗既曰如上所云。则其蔚然而有兴也不难矣。何也。朱夫子尝论秦俗之强悍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王临川论七月之诗。以为不作无益。不贵异物。而致美乎田桑之事。女不淫而仁也。士不惰而武也。今灵以尚强武勤稼穑之俗。而赵侯又以学校之政道之。则其始乎七月忠爱之厚。而骎骎乎二南修齐之化也。吾将翘足而待之矣。灵之士其勉之哉。重修之役。始于某年某月。讫于某年某月。监董者县士某某也。庑享安文成。其名以本朝 御讳。今年月日。因朝旨改从其旧名云。乙巳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2L 页
 七月日。恩津宋时烈记。
七月日。恩津宋时烈记。洪阳县爱莲堂记
人固未尝无爱也。惟得其所爱者为难也。且人心如面不同。而各随其心之所当而爱焉。其所爱之不同也无惑也。然其于草木则芳臭之自别。而人以公眼品题于其间。则宜无所不同者。然濂溪先生称李唐人爱牧(一作牡)丹。晋处士爱菊。而至于莲也则既名之以君子。而叹无同己而爱之者。呜呼。郭巾之垫雨也。而洛阳垂于晴。谢鼻之鼽芥也。而江东拥于吟。汉晋之俗尚如彼。而至于宋也。顾乃如此何也。岂时序之渐下而然耶。洪阳县监李侯子重。名其官沼之堂曰爱莲。斯可谓得其所爱。而趣同于古贤矣。盖子重自其大王父龟川君。以河间东平之德。当废朝昏浊之时。痛念国家之将亡。倡率宗盟。忘身立慬。卒以扶植彝伦。而子重学于家庭。律己自守。不苟于进取。是盖将自为君子。而为人之所爱矣。其慕古贤而爱其所名者。奚足言哉。虽然濂溪之可慕者。有大于此者。其建图属书。阐阴阳造化之妙。则其文固可读也。至其为政则朱子称其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心(心恐误)新学校。以教其人。而荒崖绝岛。不惮瘴毒之侵。缓视徐按。惟以洗冤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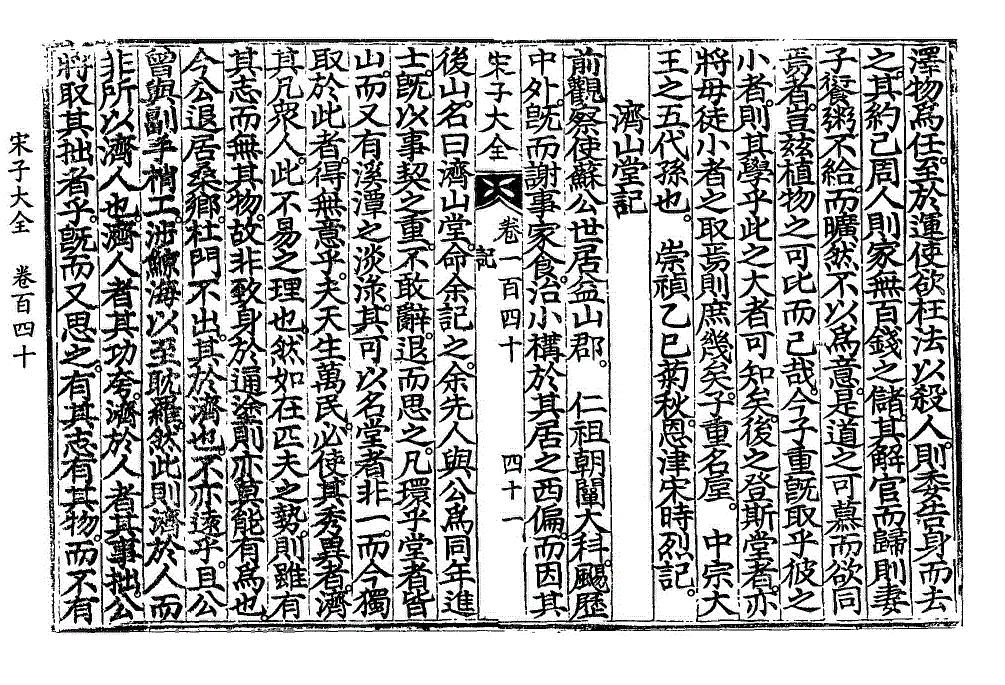 泽物为任。至于运使欲枉法以杀人。则委告身而去之。其约己周人则家无百钱之储。其解官而归则妻子餰粥不给。而旷然不以为意。是道之可慕而欲同焉者。岂玆植物之可比而已哉。今子重既取乎彼之小者。则其学乎此之大者可知矣。后之登斯堂者。亦将毋徒小者之取焉则庶几矣。子重名垕。 中宗大王之五代孙也。 崇祯乙巳菊秋。恩津宋时烈记。
泽物为任。至于运使欲枉法以杀人。则委告身而去之。其约己周人则家无百钱之储。其解官而归则妻子餰粥不给。而旷然不以为意。是道之可慕而欲同焉者。岂玆植物之可比而已哉。今子重既取乎彼之小者。则其学乎此之大者可知矣。后之登斯堂者。亦将毋徒小者之取焉则庶几矣。子重名垕。 中宗大王之五代孙也。 崇祯乙巳菊秋。恩津宋时烈记。济山堂记
前观察使苏公世居益山郡。 仁祖朝阐大科。飏历中外。既而谢事家食。治小构于其居之西偏。而因其后山。名曰济山堂。命余记之。余先人与公为同年进士。既以事契之重。不敢辞。退而思之。凡环乎堂者皆山。而又有溪潭之淡渌。其可以名堂者非一。而今独取于此者。得无意乎。夫天生万民。必使其秀异者。济其凡众人。此不易之理也。然如在匹夫之势。则虽有其志而无其物。故非致身于通涂则亦莫能有为也。今公退居桑乡。杜门不出。其于济也。不亦远乎。且公曾与副手梢工。涉鲸海以至耽罗。然此则济于人而非所以济人也。济人者其功夸。济于人者其事拙。公将取其拙者乎。既而又思之。有其志有其物。而不有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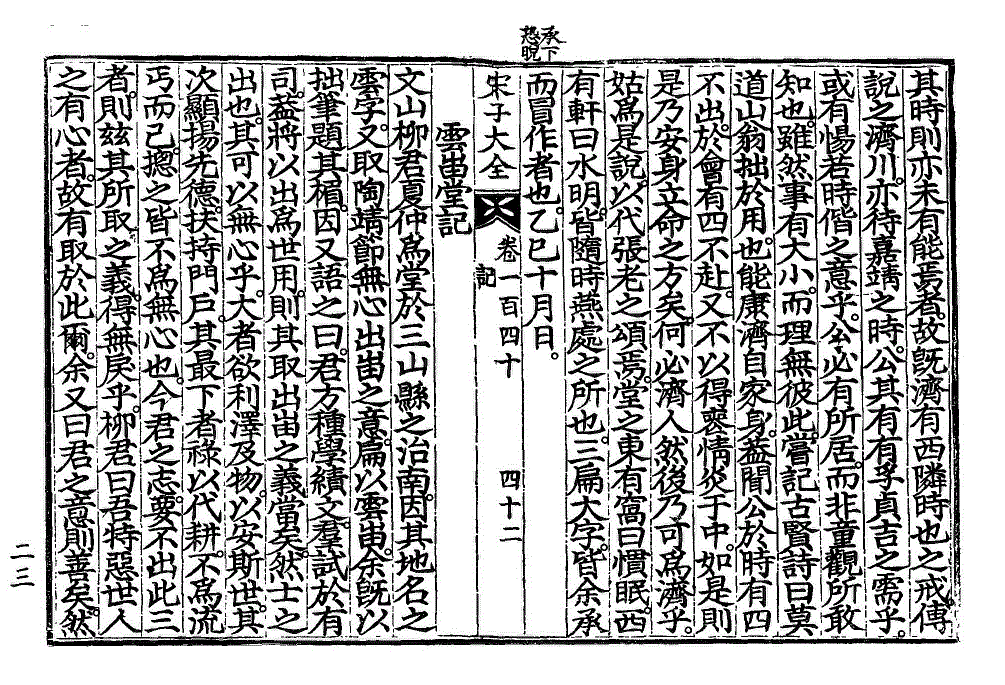 其时则亦未有能焉者。故既济有西邻时也之戒。傅说之济川。亦待嘉靖之时。公其有有孚贞吉之需乎。或有惕若时偕之意乎。公必有所居。而非童观所敢知也。虽然事有大小。而理无彼此。尝记古贤诗曰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盖闻公于时有四不出。于会有四不赴。又不以得丧情炎于中。如是则是乃安身立命之方矣。何必济人然后乃可为济乎。姑为是说。以代张老之颂焉。堂之东有窝曰惯眠。西有轩曰水明。皆随时燕处之所也。三扁大字。皆余承(承下恐脱)而冒作者也。乙巳十月日。
其时则亦未有能焉者。故既济有西邻时也之戒。傅说之济川。亦待嘉靖之时。公其有有孚贞吉之需乎。或有惕若时偕之意乎。公必有所居。而非童观所敢知也。虽然事有大小。而理无彼此。尝记古贤诗曰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盖闻公于时有四不出。于会有四不赴。又不以得丧情炎于中。如是则是乃安身立命之方矣。何必济人然后乃可为济乎。姑为是说。以代张老之颂焉。堂之东有窝曰惯眠。西有轩曰水明。皆随时燕处之所也。三扁大字。皆余承(承下恐脱)而冒作者也。乙巳十月日。云岫堂记
文山柳君夏仲为堂于三山县之治南。因其地名之云字。又取陶靖节无心出岫之意。扁以云岫。余既以拙笔题其楣。因又语之曰。君方种学绩文。群试于有司。盖将以出为世用。则其取出岫之义当矣。然士之出也。其可以无心乎。大者欲利泽及物。以安斯世。其次显扬先德。扶持门户。其最下者禄以代耕。不为流丐而已。总之皆不为无心也。今君之志。要不出此三者。则玆其所取之义。得无戾乎。柳君曰吾特恶世人之有心者。故有取于此尔。余又曰君之意则善矣。然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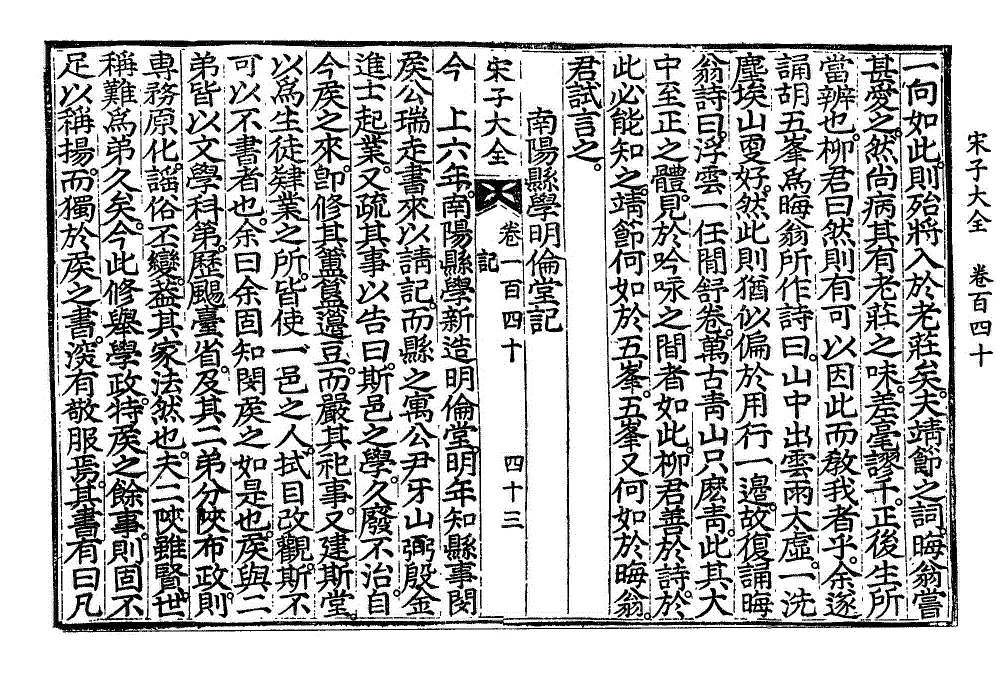 一向如此。则殆将入于老庄矣。夫靖节之词。晦翁尝甚爱之。然尚病其有老庄之味。差毫谬千。正后生所当辨也。柳君曰然则有可以因此而教我者乎。余遂诵胡五峰为晦翁所作诗曰。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然此则犹似偏于用行一边。故复诵晦翁诗曰。浮云一任閒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此其大中至正之体。见于吟咏之间者如此。柳君善于诗。于此必能知之。靖节何如于五峰。五峰又何如于晦翁。君试言之。
一向如此。则殆将入于老庄矣。夫靖节之词。晦翁尝甚爱之。然尚病其有老庄之味。差毫谬千。正后生所当辨也。柳君曰然则有可以因此而教我者乎。余遂诵胡五峰为晦翁所作诗曰。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然此则犹似偏于用行一边。故复诵晦翁诗曰。浮云一任閒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此其大中至正之体。见于吟咏之间者如此。柳君善于诗。于此必能知之。靖节何如于五峰。五峰又何如于晦翁。君试言之。南阳县学明伦堂记
今 上六年。南阳县学新造明伦堂。明年知县事闵侯公瑞走书来以请记。而县之寓公尹牙山弼殷,金进士起业。又疏其事以告曰。斯邑之学。久废不治。自今侯之来。即修其簠簋笾豆。而严其祀事。又建斯堂。以为生徒肄业之所。皆使一邑之人。拭目改观。斯不可以不书者也。余曰余固知闵侯之如是也。侯与二弟皆以文学科第。历飏台省。及其二弟分陕布政。则专务原化。谣俗丕变。盖其家法然也。夫二陕虽贤。世称难为弟久矣。今此修举学政。特侯之馀事。则固不足以称扬。而独于侯之书。深有敬服焉。其书有曰凡
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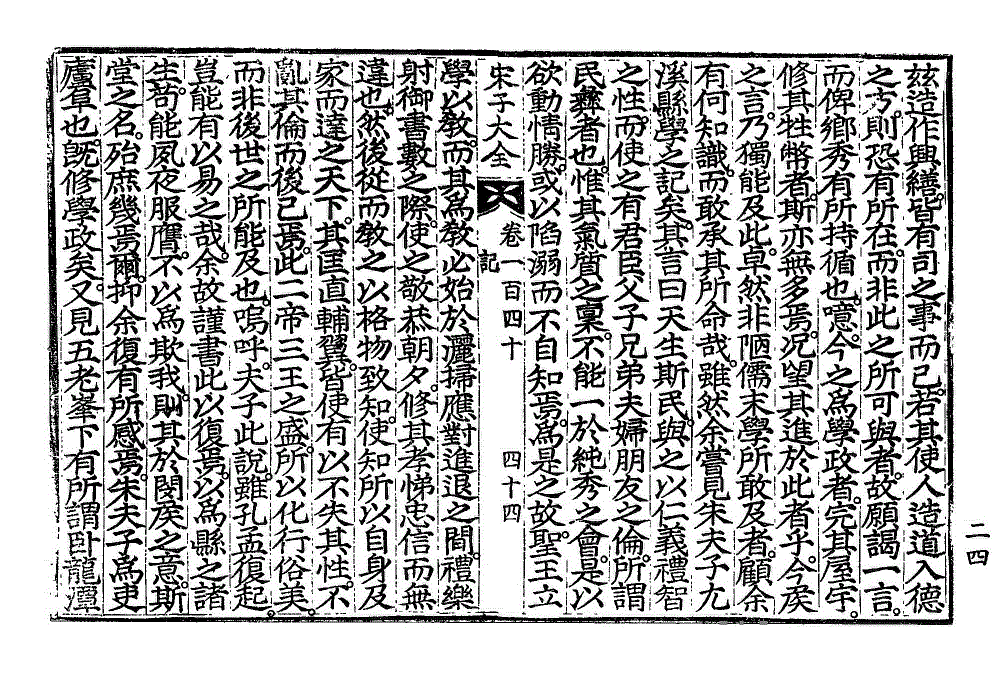 玆造作兴缮。皆有司之事而已。若其使人造道入德之方。则恐有所在。而非此之所可与者。故愿谒一言。而俾乡秀有所持循也。噫。今之为学政者。完其屋宇。修其牲币者。斯亦无多焉。况望其进于此者乎。今侯之言。乃独能及此。卓然非陋儒末学所敢及者。顾余有何知识。而敢承其所命哉。虽然余尝见朱夫子尤溪县学之记矣。其言曰天生斯民。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所谓民彝者也。惟其气质之禀。不能一于纯秀之会。是以欲动情胜。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为是之故。圣王立学以教。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以格物致知。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而达之天下。其匡直辅翼。皆使有以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呜呼。夫子此说。虽孔孟复起。岂能有以易之哉。余故谨书此以复焉。以为县之诸生。苟能夙夜服膺。不以为欺我。则其于闵侯之意。斯堂之名。殆庶几焉尔。抑余复有所感焉。朱夫子为吏庐阜也。既修学政矣。又见五老峰下有所谓卧龙潭
玆造作兴缮。皆有司之事而已。若其使人造道入德之方。则恐有所在。而非此之所可与者。故愿谒一言。而俾乡秀有所持循也。噫。今之为学政者。完其屋宇。修其牲币者。斯亦无多焉。况望其进于此者乎。今侯之言。乃独能及此。卓然非陋儒末学所敢及者。顾余有何知识。而敢承其所命哉。虽然余尝见朱夫子尤溪县学之记矣。其言曰天生斯民。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所谓民彝者也。惟其气质之禀。不能一于纯秀之会。是以欲动情胜。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为是之故。圣王立学以教。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以格物致知。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而达之天下。其匡直辅翼。皆使有以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呜呼。夫子此说。虽孔孟复起。岂能有以易之哉。余故谨书此以复焉。以为县之诸生。苟能夙夜服膺。不以为欺我。则其于闵侯之意。斯堂之名。殆庶几焉尔。抑余复有所感焉。朱夫子为吏庐阜也。既修学政矣。又见五老峰下有所谓卧龙潭宋子大全卷一百四十 第 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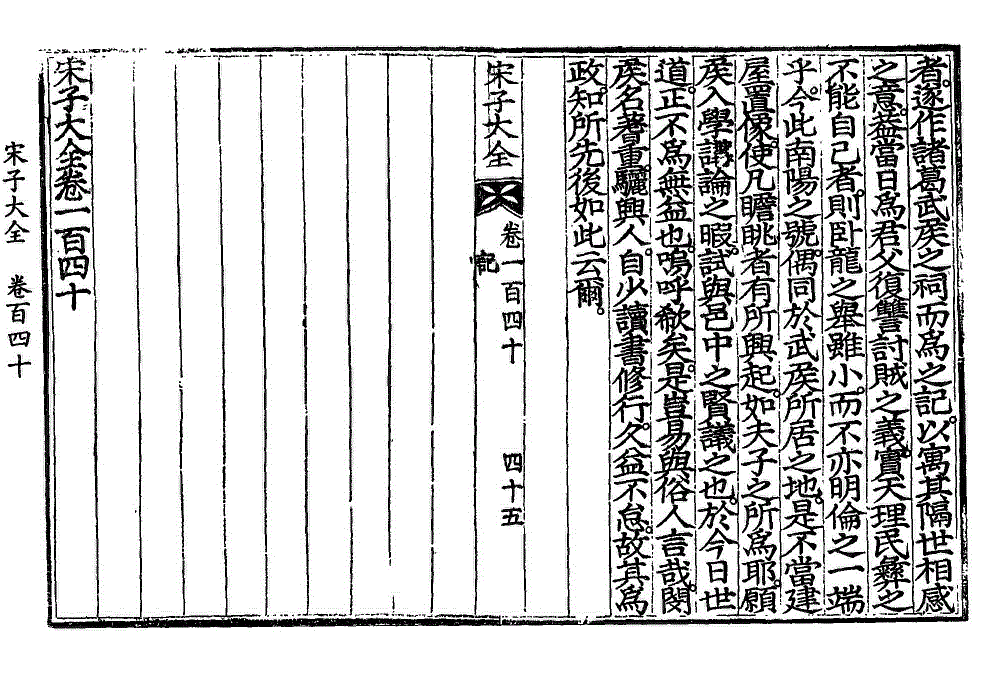 者。遂作诸葛武侯之祠而为之记。以寓其隔世相感之意。盖当日为君父复雠讨贼之义。实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者。则卧龙之举虽小。而不亦明伦之一端乎。今此南阳之号。偶同于武侯所居之地。是不当建屋置像。使凡瞻眺者有所兴起。如夫子之所为耶。愿侯入学讲论之暇。试与邑中之贤议之也。于今日世道。正不为无益也。呜呼欷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闵侯名蓍重。骊兴人。自少读书修行。久益不怠。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如此云尔。
者。遂作诸葛武侯之祠而为之记。以寓其隔世相感之意。盖当日为君父复雠讨贼之义。实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者。则卧龙之举虽小。而不亦明伦之一端乎。今此南阳之号。偶同于武侯所居之地。是不当建屋置像。使凡瞻眺者有所兴起。如夫子之所为耶。愿侯入学讲论之暇。试与邑中之贤议之也。于今日世道。正不为无益也。呜呼欷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闵侯名蓍重。骊兴人。自少读书修行。久益不怠。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如此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