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x 页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论田制(六条)
论田制(六条)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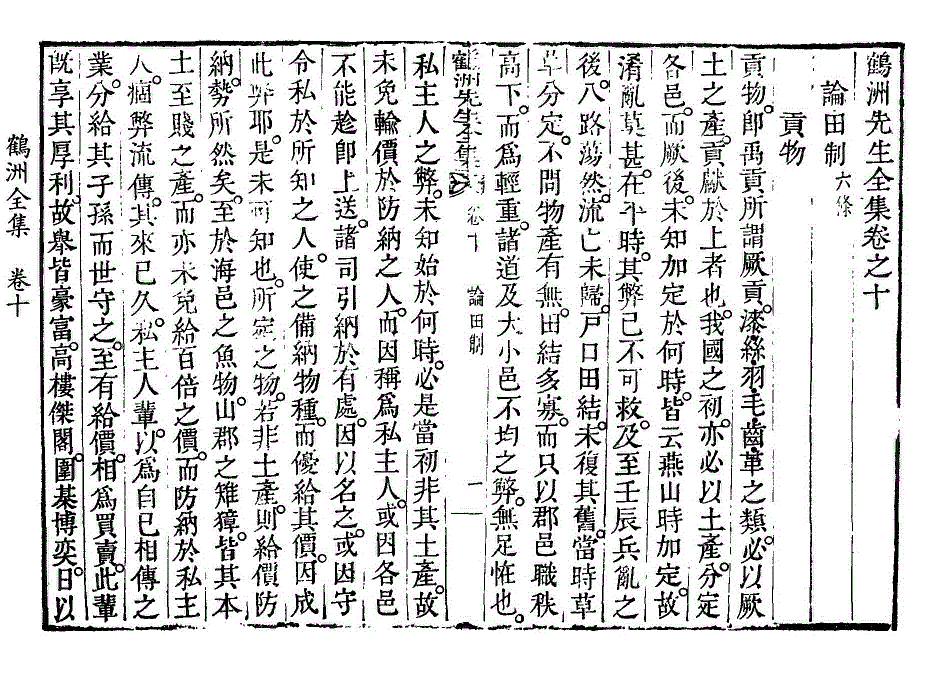 贡物
贡物贡物。即禹贡所谓厥贡。漆,丝,羽,毛,齿,革之类。必以厥土之产。贡献于上者也。我国之初。亦必以土产。分定各邑。而厥后。未知加定于何时。皆云燕山时加定。故淆乱莫甚。在平时。其弊已不可救。及至壬辰兵乱之后。八路荡然。流亡未归。户口田结。未复其旧。当时草草分定。不问物产有无。田结多寡。而只以郡邑职秩高下。而为轻重。诸道及大小邑不均之弊。无足怪也。私主人之弊。未知始于何时。必是当初非其土产。故未免输价于防纳之人。而因称为私主人。或因各邑不能趁即上送。诸司引纳于有处。因以名之。或因守令私于所知之人。使之备纳物种。而优给其价。因成此弊耶。是未可知也。所定之物。若非土产。则给价防纳。势所然矣。至于海邑之鱼物。山郡之雉獐。皆其本土至贱之产。而亦未免给百倍之价。而防纳于私主人。痼弊流传。其来已久。私主人辈。以为自己相传之业。分给其子孙而世守之。至有给价。相为买卖。此辈既享其厚利。故举皆豪富。高楼杰阁。围棋博奕。日以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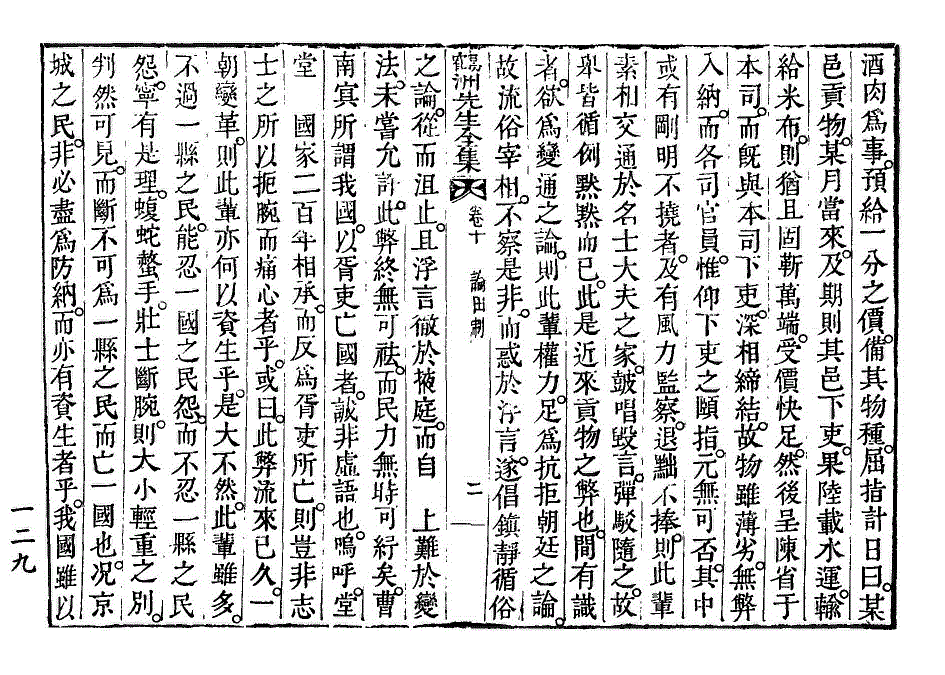 酒肉为事。预给一分之价。备其物种。屈指计日曰。某邑贡物。某月当来。及期则其邑下吏。果陆载水运。输给米布。则犹且固靳万端。受价快足。然后呈陈省于本司。而既与本司下吏。深相缔结。故物虽薄劣。无弊入纳。而各司官员。惟仰下吏之颐指。元无可否。其中或有刚明不挠者。及有风力监察。退黜不捧。则此辈素相交通于名士大夫之家。鼓唱毁言。弹驳随之。故举皆循例默默而已。此是近来贡物之弊也。间有识者。欲为变通之论。则此辈权力。足为抗拒朝廷之论。故流俗宰相。不察是非。而惑于浮言。遂倡镇静循俗之论。从而沮止。且浮言彻于掖庭。而自 上难于变法。未尝允许。此弊终无可祛。而民力无时可纾矣。曹南冥所谓我国。以胥吏亡国者。诚非虚语也。呜呼。堂堂 国家二百年相承。而反为胥吏所亡。则岂非志士之所以扼腕而痛心者乎。或曰。此弊流来已久。一朝变革。则此辈亦何以资生乎。是大不然。此辈虽多。不过一县之民。能忍一国之民怨。而不忍一县之民怨。宁有是理。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则大小轻重之别。判然可见。而断不可为一县之民而亡一国也。况京城之民。非必尽为防纳。而亦有资生者乎。我国虽以
酒肉为事。预给一分之价。备其物种。屈指计日曰。某邑贡物。某月当来。及期则其邑下吏。果陆载水运。输给米布。则犹且固靳万端。受价快足。然后呈陈省于本司。而既与本司下吏。深相缔结。故物虽薄劣。无弊入纳。而各司官员。惟仰下吏之颐指。元无可否。其中或有刚明不挠者。及有风力监察。退黜不捧。则此辈素相交通于名士大夫之家。鼓唱毁言。弹驳随之。故举皆循例默默而已。此是近来贡物之弊也。间有识者。欲为变通之论。则此辈权力。足为抗拒朝廷之论。故流俗宰相。不察是非。而惑于浮言。遂倡镇静循俗之论。从而沮止。且浮言彻于掖庭。而自 上难于变法。未尝允许。此弊终无可祛。而民力无时可纾矣。曹南冥所谓我国。以胥吏亡国者。诚非虚语也。呜呼。堂堂 国家二百年相承。而反为胥吏所亡。则岂非志士之所以扼腕而痛心者乎。或曰。此弊流来已久。一朝变革。则此辈亦何以资生乎。是大不然。此辈虽多。不过一县之民。能忍一国之民怨。而不忍一县之民怨。宁有是理。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则大小轻重之别。判然可见。而断不可为一县之民而亡一国也。况京城之民。非必尽为防纳。而亦有资生者乎。我国虽以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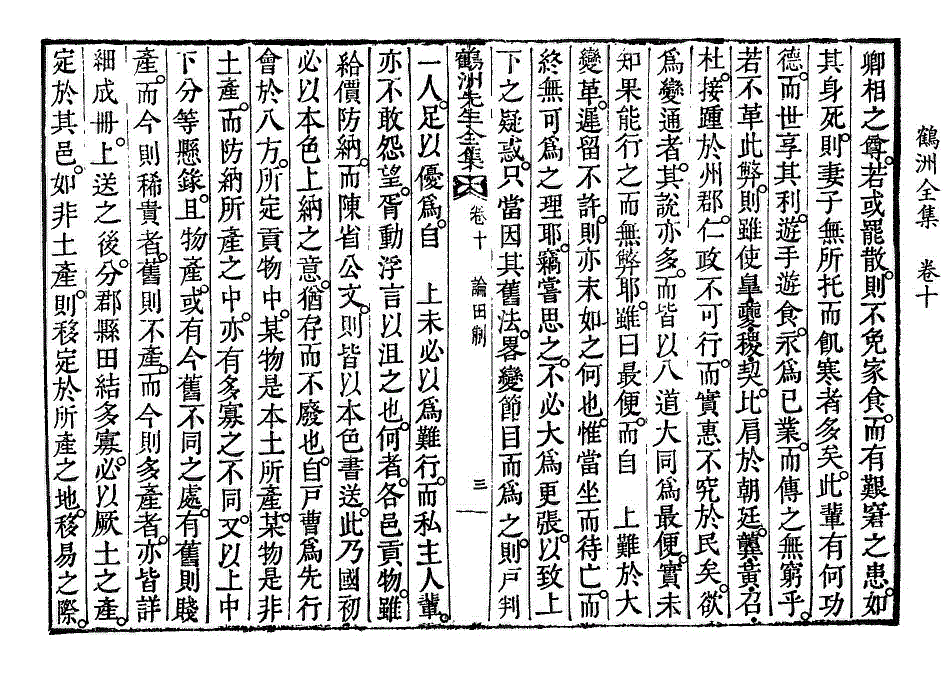 卿相之尊。若或罢散。则不免家食。而有艰窘之患。如其身死。则妻子无所托而饥寒者多矣。此辈有何功德。而世享其利。游手游食。永为己业。而传之无穷乎。若不革此弊。则虽使皋,夔,稷,契。比肩于朝廷。龚,黄,召,杜。接踵于州郡。仁政不可行。而实惠不究于民矣。欲为变通者。其说亦多。而皆以八道大同为最便。实未知果能行之而无弊耶。虽曰最便。而自 上难于大变革。迟留不许。则亦末如之何也。惟当坐而待亡。而终无可为之理耶。窃尝思之。不必大为更张。以致上下之疑惑。只当因其旧法。略变节目而为之。则户判一人。足以优为。自 上未必以为难行。而私主人辈。亦不敢怨望。胥动浮言以沮之也。何者。各邑贡物。虽给价防纳。而陈省公文。则皆以本色书送。此乃国初必以本色上纳之意。犹存而不废也。自户曹为先行会于八方。所定贡物中。某物是本土所产。某物是非土产。而防纳所产之中。亦有多寡之不同。又以上中下分等悬录。且物产。或有今旧不同之处。有旧则贱产。而今则稀贵者。旧则不产。而今则多产者。亦皆详细成册。上送之后。分郡县田结多寡。必以厥土之产。定于其邑。如非土产。则移定于所产之地。移易之际。
卿相之尊。若或罢散。则不免家食。而有艰窘之患。如其身死。则妻子无所托而饥寒者多矣。此辈有何功德。而世享其利。游手游食。永为己业。而传之无穷乎。若不革此弊。则虽使皋,夔,稷,契。比肩于朝廷。龚,黄,召,杜。接踵于州郡。仁政不可行。而实惠不究于民矣。欲为变通者。其说亦多。而皆以八道大同为最便。实未知果能行之而无弊耶。虽曰最便。而自 上难于大变革。迟留不许。则亦末如之何也。惟当坐而待亡。而终无可为之理耶。窃尝思之。不必大为更张。以致上下之疑惑。只当因其旧法。略变节目而为之。则户判一人。足以优为。自 上未必以为难行。而私主人辈。亦不敢怨望。胥动浮言以沮之也。何者。各邑贡物。虽给价防纳。而陈省公文。则皆以本色书送。此乃国初必以本色上纳之意。犹存而不废也。自户曹为先行会于八方。所定贡物中。某物是本土所产。某物是非土产。而防纳所产之中。亦有多寡之不同。又以上中下分等悬录。且物产。或有今旧不同之处。有旧则贱产。而今则稀贵者。旧则不产。而今则多产者。亦皆详细成册。上送之后。分郡县田结多寡。必以厥土之产。定于其邑。如非土产。则移定于所产之地。移易之际。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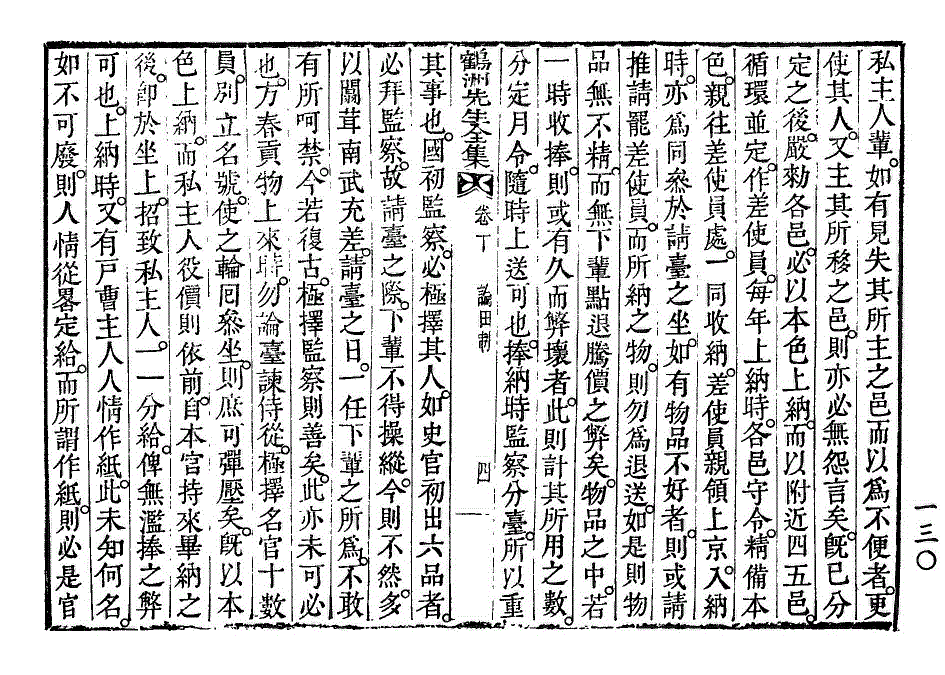 私主人辈。如有见失其所主之邑而以为不便者。更使其人。又主其所移之邑。则亦必无怨言矣。既已分定之后。严敕各邑。必以本色上纳。而以附近四五邑。循环并定。作差使员。每年上纳时。各邑守令。精备本色。亲往差使员处。一同收纳。差使员亲领上京。入纳时。亦为同参于请台之坐。如有物品不好者。则或请推请罢差使员。而所纳之物。则勿为退送。如是则物品无不精。而无下辈点退腾价之弊矣。物品之中。若一时收捧。则或有久而弊坏者。此则计其所用之数。分定月令。随时上送可也。捧纳时监察分台。所以重其事也。国初监察。必极择其人。如史官初出六品者。必拜监察。故请台之际。下辈不得操纵。今则不然。多以阘茸南武充差。请台之日。一任下辈之所为。不敢有所呵禁。今若复古。极择监察则善矣。此亦未可必也。方春贡物上来时。勿论台谏侍从。极择名官十数员。别立名号。使之轮回参坐。则庶可弹压矣。既以本色上纳。而私主人役价则依前。自本官持来毕纳之后。即于坐上。招致私主人。一一分给。俾无滥捧之弊可也。上纳时。又有户曹主人人情作纸。此未知何名。如不可废。则人情从略定给。而所谓作纸。则必是官
私主人辈。如有见失其所主之邑而以为不便者。更使其人。又主其所移之邑。则亦必无怨言矣。既已分定之后。严敕各邑。必以本色上纳。而以附近四五邑。循环并定。作差使员。每年上纳时。各邑守令。精备本色。亲往差使员处。一同收纳。差使员亲领上京。入纳时。亦为同参于请台之坐。如有物品不好者。则或请推请罢差使员。而所纳之物。则勿为退送。如是则物品无不精。而无下辈点退腾价之弊矣。物品之中。若一时收捧。则或有久而弊坏者。此则计其所用之数。分定月令。随时上送可也。捧纳时监察分台。所以重其事也。国初监察。必极择其人。如史官初出六品者。必拜监察。故请台之际。下辈不得操纵。今则不然。多以阘茸南武充差。请台之日。一任下辈之所为。不敢有所呵禁。今若复古。极择监察则善矣。此亦未可必也。方春贡物上来时。勿论台谏侍从。极择名官十数员。别立名号。使之轮回参坐。则庶可弹压矣。既以本色上纳。而私主人役价则依前。自本官持来毕纳之后。即于坐上。招致私主人。一一分给。俾无滥捧之弊可也。上纳时。又有户曹主人人情作纸。此未知何名。如不可废。则人情从略定给。而所谓作纸。则必是官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1H 页
 员之所捧。其果补用于国乎。抑亦其所私用乎。虽补用于国。利少而害多。则减之可也。况是私用。则是亦不可以己乎。其中。又有不可不变通者。诸各司。既知此辈享其厚利。凡司中使唤杂役。莫不责办。非徒私事。亦有公事如褒贬时设馔。各司皆然。而至有礼葬军,藏冰军,担持军,轿军,马草驱债。饯送时酒馔。监察月令各 陵差祭时。刷马人夫炬烛及其他细琐之事。难以毛举。而皆责出于私主人。故私主人辈。亦不胜其苦。其所谓役价。必指此等事而言也。非但本司之役。亦有户曹之役如设场时。试官供馈。虽定应办官。而计减物件甚少。故为应办官者。督责于贡物主人。罔有记极。此乃苦役之尤甚者也。设场。国家之盛举。而试官。乃寄食于贡物主人。岂不寒心哉。此则必须复设礼宾而可罢者也。诸般苦役如此。故私主人辈。必欲得百倍之价。刀腾操纵。无所不至。或纳赂潜图。或受简请嘱。或临急阻搪。虽甚凶年。必捧丰年之价者。渠亦有执言之地故也。此无他。诸各司及户曹。盖诲之益其盗也。如欲变通贡物之弊。必须先减私主人之杂役。若夺其防纳之利。而苦役犹夫前日。则私主人。亦吾民也。其何以保存乎。自户曹严立事目
员之所捧。其果补用于国乎。抑亦其所私用乎。虽补用于国。利少而害多。则减之可也。况是私用。则是亦不可以己乎。其中。又有不可不变通者。诸各司。既知此辈享其厚利。凡司中使唤杂役。莫不责办。非徒私事。亦有公事如褒贬时设馔。各司皆然。而至有礼葬军,藏冰军,担持军,轿军,马草驱债。饯送时酒馔。监察月令各 陵差祭时。刷马人夫炬烛及其他细琐之事。难以毛举。而皆责出于私主人。故私主人辈。亦不胜其苦。其所谓役价。必指此等事而言也。非但本司之役。亦有户曹之役如设场时。试官供馈。虽定应办官。而计减物件甚少。故为应办官者。督责于贡物主人。罔有记极。此乃苦役之尤甚者也。设场。国家之盛举。而试官。乃寄食于贡物主人。岂不寒心哉。此则必须复设礼宾而可罢者也。诸般苦役如此。故私主人辈。必欲得百倍之价。刀腾操纵。无所不至。或纳赂潜图。或受简请嘱。或临急阻搪。虽甚凶年。必捧丰年之价者。渠亦有执言之地故也。此无他。诸各司及户曹。盖诲之益其盗也。如欲变通贡物之弊。必须先减私主人之杂役。若夺其防纳之利。而苦役犹夫前日。则私主人。亦吾民也。其何以保存乎。自户曹严立事目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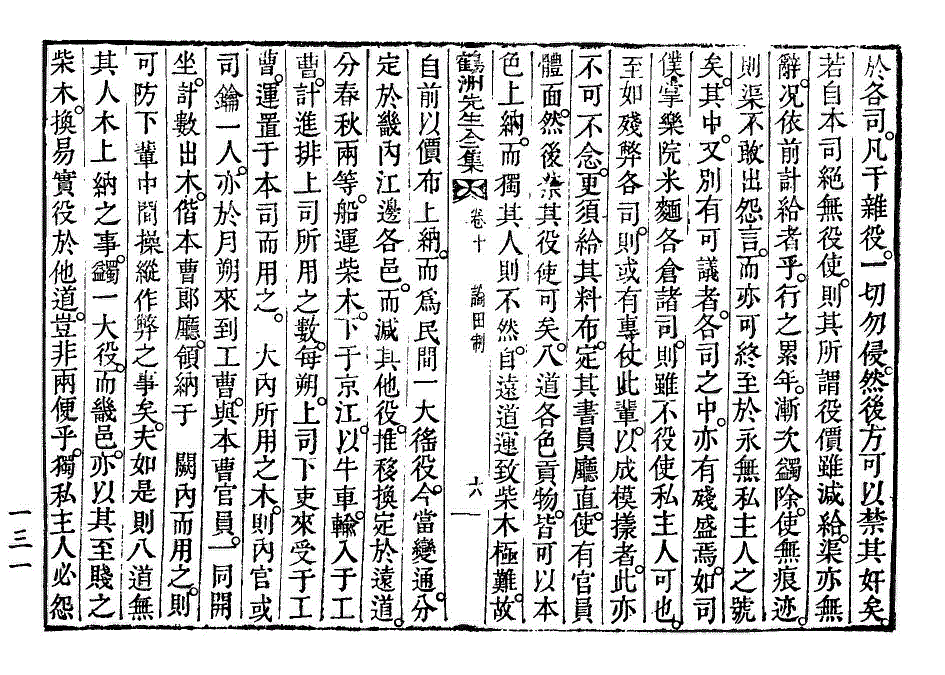 于各司。凡干杂役。一切勿侵。然后方可以禁其奸矣。若自本司绝无役使。则其所谓役价虽减给。渠亦无辞。况依前计给者乎。行之累年。渐次蠲除。使无痕迹。则渠不敢出怨言。而亦可终至于永无私主人之号矣。其中。又别有可议者。各司之中。亦有残盛焉。如司仆,掌乐院米面各仓诸司。则虽不役使私主人可也。至如残弊各司。则或有专仗此辈。以成模样者。此亦不可不念。更须给其料布。定其书员厅直。使有官员体面。然后禁其役使可矣。八道各色贡物。皆可以本色上纳。而独其人则不然。自远道运致柴木极难。故自前以价布上纳。而为民间一大徭役。今当变通。分定于畿内江边各邑。而减其他役。推移换定于远道。分春秋两等。船运柴木。下于京江。以牛车。输入于工曹。计进排上司所用之数。每朔。上司下吏来受于工曹。运置于本司而用之。 大内所用之木。则内官或司钥一人。亦于月朔来到工曹。与本曹官员。一同开坐。计数出木。偕本曹郎厅。领纳于 阙内而用之。则可防下辈中间操纵作弊之事矣。夫如是则八道无其人木上纳之事。蠲一大役。而畿邑。亦以其至贱之柴木。换易实役于他道。岂非两便乎。独私主人必怨
于各司。凡干杂役。一切勿侵。然后方可以禁其奸矣。若自本司绝无役使。则其所谓役价虽减给。渠亦无辞。况依前计给者乎。行之累年。渐次蠲除。使无痕迹。则渠不敢出怨言。而亦可终至于永无私主人之号矣。其中。又别有可议者。各司之中。亦有残盛焉。如司仆,掌乐院米面各仓诸司。则虽不役使私主人可也。至如残弊各司。则或有专仗此辈。以成模样者。此亦不可不念。更须给其料布。定其书员厅直。使有官员体面。然后禁其役使可矣。八道各色贡物。皆可以本色上纳。而独其人则不然。自远道运致柴木极难。故自前以价布上纳。而为民间一大徭役。今当变通。分定于畿内江边各邑。而减其他役。推移换定于远道。分春秋两等。船运柴木。下于京江。以牛车。输入于工曹。计进排上司所用之数。每朔。上司下吏来受于工曹。运置于本司而用之。 大内所用之木。则内官或司钥一人。亦于月朔来到工曹。与本曹官员。一同开坐。计数出木。偕本曹郎厅。领纳于 阙内而用之。则可防下辈中间操纵作弊之事矣。夫如是则八道无其人木上纳之事。蠲一大役。而畿邑。亦以其至贱之柴木。换易实役于他道。岂非两便乎。独私主人必怨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2H 页
 其失利。此亦依前给其役价可也。若然则不必八道大同。而贡物防纳之弊。岂不可以变通乎。必以土产上纳。则虽不费价。亦可备得。而品物精好。必愈于防纳之时。民之应役。反轻于八道大同之数也。自前陈省。皆书本色。则今以本色上纳。非变法也。乃旧法也。遵行旧法。有何禀 旨更定之事乎。自 上所难者。乃变法也。若行旧法。则虽或上达。亦无不 允之理矣。其中物产有无移定。及四五邑并定差员。别择名官。上纳时同参之事。似是新规。然既以本色。书于陈省。则必以土产。推移分定。乃是 祖宗立法之本意。善为上达。必无不从。并定差员。则即今小小之役。亦令差员领来。此亦有何不可。别择名官者。必欲痛革此弊。而弹压下吏之奸滥。若使同参。则有益于国。如曰非便。则不行亦可也。贡物变通之策。止于此矣。而户曹亦有巨弊。不可不知也。沿海贡物作米。想必于当初。因经用浩烦。一年所入。不能支出。故户曹抄出若干条。依详定木匹之数。而作米上纳。减给私主人。而以其所馀。补用经费。此虽出于一时不得已之计。户曹实自开防纳之路。其何以禁小民之防纳。而所定一匹之价。凶年亦不下八斗。既曰上纳。则米品颇
其失利。此亦依前给其役价可也。若然则不必八道大同。而贡物防纳之弊。岂不可以变通乎。必以土产上纳。则虽不费价。亦可备得。而品物精好。必愈于防纳之时。民之应役。反轻于八道大同之数也。自前陈省。皆书本色。则今以本色上纳。非变法也。乃旧法也。遵行旧法。有何禀 旨更定之事乎。自 上所难者。乃变法也。若行旧法。则虽或上达。亦无不 允之理矣。其中物产有无移定。及四五邑并定差员。别择名官。上纳时同参之事。似是新规。然既以本色。书于陈省。则必以土产。推移分定。乃是 祖宗立法之本意。善为上达。必无不从。并定差员。则即今小小之役。亦令差员领来。此亦有何不可。别择名官者。必欲痛革此弊。而弹压下吏之奸滥。若使同参。则有益于国。如曰非便。则不行亦可也。贡物变通之策。止于此矣。而户曹亦有巨弊。不可不知也。沿海贡物作米。想必于当初。因经用浩烦。一年所入。不能支出。故户曹抄出若干条。依详定木匹之数。而作米上纳。减给私主人。而以其所馀。补用经费。此虽出于一时不得已之计。户曹实自开防纳之路。其何以禁小民之防纳。而所定一匹之价。凶年亦不下八斗。既曰上纳。则米品颇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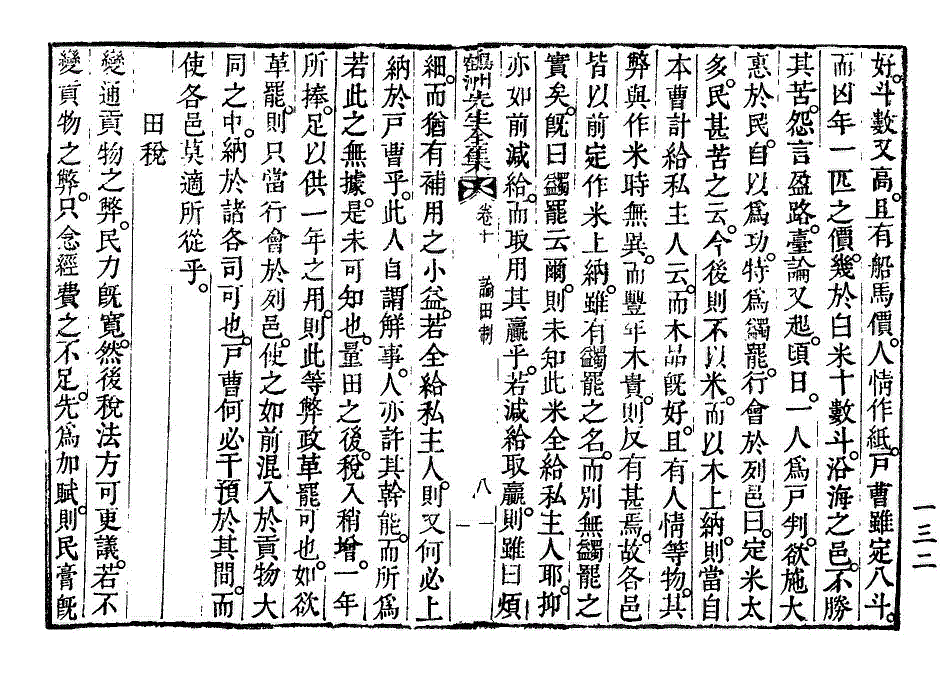 好。斗数又高。且有船马价。人情作纸。户曹虽定八斗。而凶年一匹之价。几于白米十数斗。沿海之邑。不胜其苦。怨言盈路。台论又起。顷日。一人为户判。欲施大惠于民。自以为功。特为蠲罢。行会于列邑曰。定米太多。民甚苦之云。今后则不以米。而以木上纳。则当自本曹计给私主人云。而木品既好。且有人情等物。其弊与作米时无异。而丰年木贵。则反有甚焉。故各邑皆以前定作米上纳。虽有蠲罢之名。而别无蠲罢之实矣。既曰蠲罢云尔。则未知此米全给私主人耶。抑亦如前减给。而取用其赢乎。若减给取赢。则虽曰烦细。而犹有补用之小益。若全给私主人。则又何必上纳于户曹乎。此人自谓解事。人亦许其干能。而所为若此之无据。是未可知也。量田之后。税入稍增。一年所捧。足以供一年之用。则此等弊政革罢可也。如欲革罢。则只当行会于列邑。使之如前混入于贡物大同之中。纳于诸各司可也。户曹何必干预于其间。而使各邑莫适所从乎。
好。斗数又高。且有船马价。人情作纸。户曹虽定八斗。而凶年一匹之价。几于白米十数斗。沿海之邑。不胜其苦。怨言盈路。台论又起。顷日。一人为户判。欲施大惠于民。自以为功。特为蠲罢。行会于列邑曰。定米太多。民甚苦之云。今后则不以米。而以木上纳。则当自本曹计给私主人云。而木品既好。且有人情等物。其弊与作米时无异。而丰年木贵。则反有甚焉。故各邑皆以前定作米上纳。虽有蠲罢之名。而别无蠲罢之实矣。既曰蠲罢云尔。则未知此米全给私主人耶。抑亦如前减给。而取用其赢乎。若减给取赢。则虽曰烦细。而犹有补用之小益。若全给私主人。则又何必上纳于户曹乎。此人自谓解事。人亦许其干能。而所为若此之无据。是未可知也。量田之后。税入稍增。一年所捧。足以供一年之用。则此等弊政革罢可也。如欲革罢。则只当行会于列邑。使之如前混入于贡物大同之中。纳于诸各司可也。户曹何必干预于其间。而使各邑莫适所从乎。田税
变通贡物之弊。民力既宽。然后税法方可更议。若不变贡物之弊。只念经费之不足。先为加赋。则民膏既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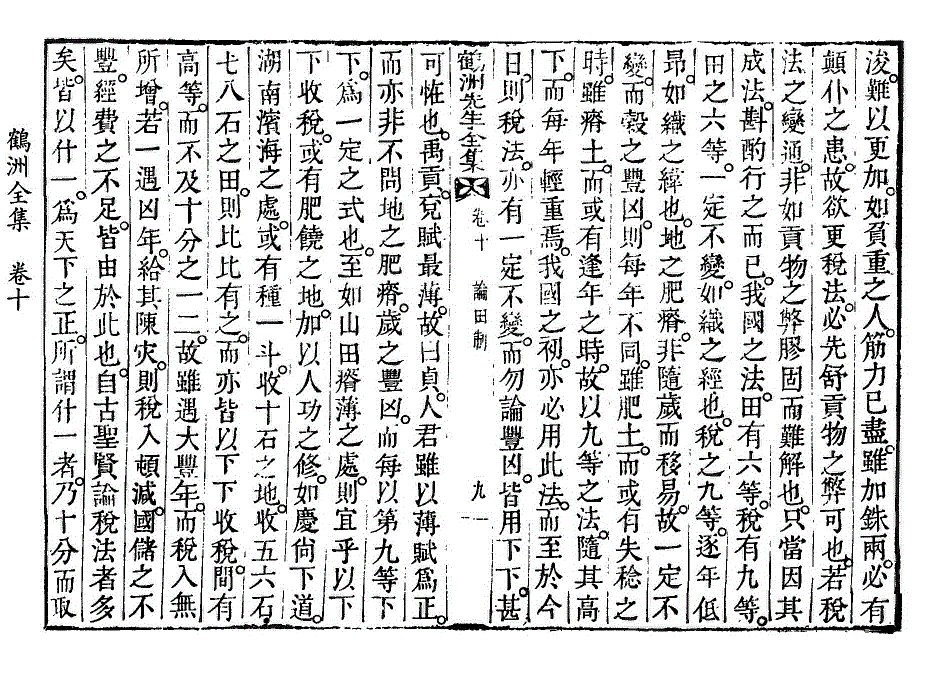 浚。难以更加。如负重之人。筋力已尽。虽加铢两。必有颠仆之患。故欲更税法。必先舒贡物之弊可也。若税法之变通。非如贡物之弊胶固而难解也。只当因其成法。斟酌行之而已。我国之法。田有六等。税有九等。田之六等。一定不变。如织之经也。税之九等。逐年低昂。如织之纬也。地之肥瘠。非随岁而移易。故一定不变。而谷之丰凶。则每年不同。虽肥土。而或有失稔之时。虽瘠土。而或有逢年之时。故以九等之法。随其高下。而每年轻重焉。我国之初。亦必用此法。而至于今日。则税法。亦有一定不变。而勿论丰凶。皆用下下。甚可怪也。禹贡。兖赋最薄。故曰贞。人君虽以薄赋为正。而亦非不问地之肥瘠。岁之丰凶。而每以第九等下下。为一定之式也。至如山田瘠薄之处。则宜乎以下下收税。或有肥饶之地。加以人功之修。如庆尚下道。湖南滨海之处。或有种一斗。收十石之地。收五六石,七八石之田。则比比有之。而亦皆以下下收税。间有高等。而不及十分之一二。故虽遇大丰年。而税入无所增。若一遇凶年。给其陈灾。则税入顿减。国储之不丰。经费之不足。皆由于此也。自古圣贤论税法者多矣。皆以什一。为天下之正。所谓什一者。乃十分而取
浚。难以更加。如负重之人。筋力已尽。虽加铢两。必有颠仆之患。故欲更税法。必先舒贡物之弊可也。若税法之变通。非如贡物之弊胶固而难解也。只当因其成法。斟酌行之而已。我国之法。田有六等。税有九等。田之六等。一定不变。如织之经也。税之九等。逐年低昂。如织之纬也。地之肥瘠。非随岁而移易。故一定不变。而谷之丰凶。则每年不同。虽肥土。而或有失稔之时。虽瘠土。而或有逢年之时。故以九等之法。随其高下。而每年轻重焉。我国之初。亦必用此法。而至于今日。则税法。亦有一定不变。而勿论丰凶。皆用下下。甚可怪也。禹贡。兖赋最薄。故曰贞。人君虽以薄赋为正。而亦非不问地之肥瘠。岁之丰凶。而每以第九等下下。为一定之式也。至如山田瘠薄之处。则宜乎以下下收税。或有肥饶之地。加以人功之修。如庆尚下道。湖南滨海之处。或有种一斗。收十石之地。收五六石,七八石之田。则比比有之。而亦皆以下下收税。间有高等。而不及十分之一二。故虽遇大丰年。而税入无所增。若一遇凶年。给其陈灾。则税入顿减。国储之不丰。经费之不足。皆由于此也。自古圣贤论税法者多矣。皆以什一。为天下之正。所谓什一者。乃十分而取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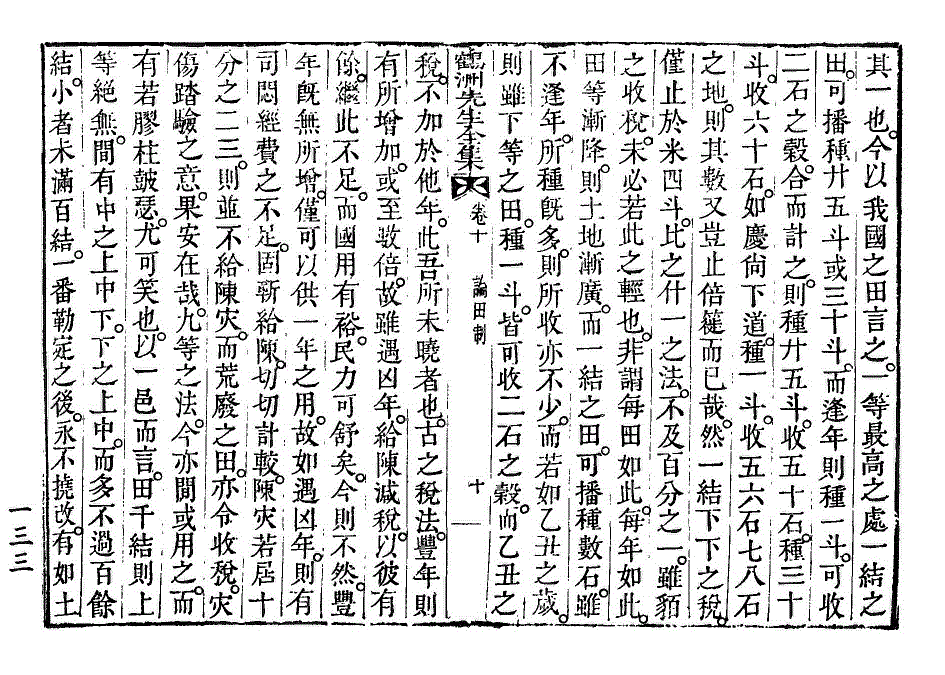 其一也。今以我国之田言之。一等最高之处一结之田。可播种廿五斗或三十斗。而逢年则种一斗。可收二石之谷。合而计之。则种廿五斗。收五十石。种三十斗。收六十石。如庆尚下道。种一斗。收五六石七八石之地。则其数又岂止倍蓰而已哉。然一结下下之税。仅止于米四斗。比之什一之法。不及百分之一。虽貊之收税。未必若此之轻也。非谓每田如此。每年如此。田等渐降。则土地渐广。而一结之田。可播种数石。虽不逢年。所种既多。则所收亦不少。而若如乙丑之岁。则虽下等之田。种一斗。皆可收二石之谷。而乙丑之税。不加于他年。此吾所未晓者也。古之税法。丰年则有所增加。或至数倍。故虽遇凶年。给陈减税。以彼有馀。继此不足。而国用有裕。民力可舒矣。今则不然。丰年既无所增。仅可以供一年之用。故如遇凶年。则有司闷经费之不足。固靳给陈。切切计较。陈灾若居十分之二三。则并不给陈灾。而荒废之田。亦令收税。灾伤踏验之意。果安在哉。九等之法。今亦间或用之。而有若胶柱鼓瑟。尤可笑也。以一邑而言。田千结则上等绝无。间有中之上中下。下之上中。而多不过百馀结。小者未满百结。一番勒定之后。永不挠改。有如土
其一也。今以我国之田言之。一等最高之处一结之田。可播种廿五斗或三十斗。而逢年则种一斗。可收二石之谷。合而计之。则种廿五斗。收五十石。种三十斗。收六十石。如庆尚下道。种一斗。收五六石七八石之地。则其数又岂止倍蓰而已哉。然一结下下之税。仅止于米四斗。比之什一之法。不及百分之一。虽貊之收税。未必若此之轻也。非谓每田如此。每年如此。田等渐降。则土地渐广。而一结之田。可播种数石。虽不逢年。所种既多。则所收亦不少。而若如乙丑之岁。则虽下等之田。种一斗。皆可收二石之谷。而乙丑之税。不加于他年。此吾所未晓者也。古之税法。丰年则有所增加。或至数倍。故虽遇凶年。给陈减税。以彼有馀。继此不足。而国用有裕。民力可舒矣。今则不然。丰年既无所增。仅可以供一年之用。故如遇凶年。则有司闷经费之不足。固靳给陈。切切计较。陈灾若居十分之二三。则并不给陈灾。而荒废之田。亦令收税。灾伤踏验之意。果安在哉。九等之法。今亦间或用之。而有若胶柱鼓瑟。尤可笑也。以一邑而言。田千结则上等绝无。间有中之上中下。下之上中。而多不过百馀结。小者未满百结。一番勒定之后。永不挠改。有如土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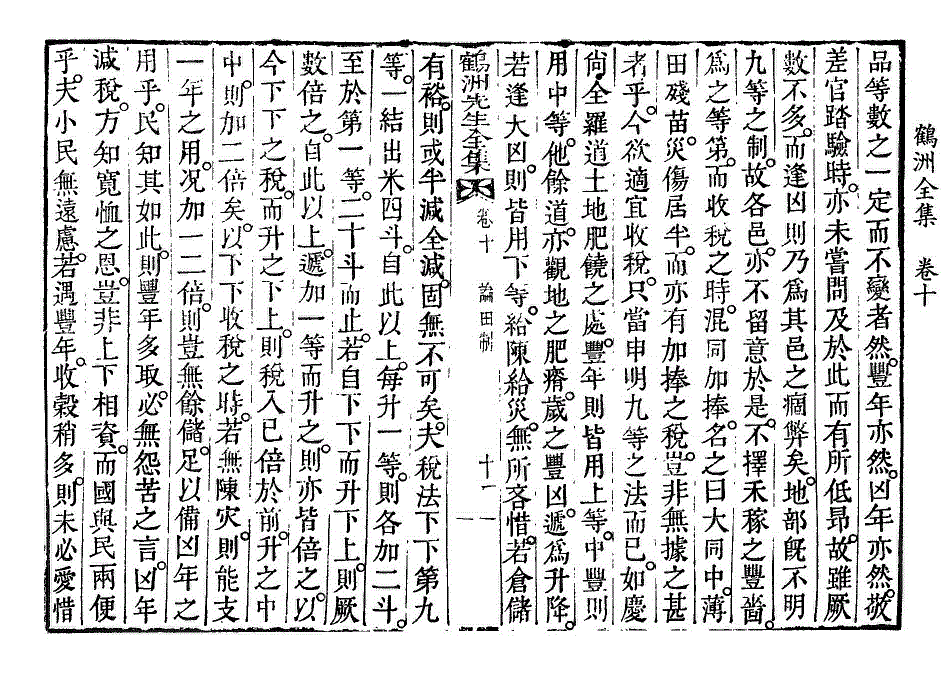 品等数之一定而不变者然。丰年亦然。凶年亦然。敬差官踏验时。亦未尝问及于此而有所低昂。故虽厥数不多。而逢凶则乃为其邑之痼弊矣。地部既不明九等之制。故各邑。亦不留意于是。不择禾稼之丰啬。为之等第。而收税之时。混同加捧。名之曰大同中。薄田残苗。灾伤居半。而亦有加捧之税。岂非无据之甚者乎。今欲适宜收税。只当申明九等之法而已。如庆尚,全罗道土地肥饶之处。丰年则皆用上等。中丰则用中等。他馀道。亦观地之肥瘠。岁之丰凶。递为升降。若逢大凶。则皆用下等。给陈给灾。无所吝惜。若仓储有裕。则或半减全减。固无不可矣。夫税法下下第九等。一结出米四斗。自此以上。每升一等。则各加二斗。至于第一等。二十斗而止。若自下下而升下上。则厥数倍之。自此以上。递加一等而升之。则亦皆倍之。以今下下之税。而升之下上。则税入已倍于前。升之中中。则加二倍矣。以下下收税之时。若无陈灾。则能支一年之用。况加一二倍。则岂无馀储。足以备凶年之用乎。民知其如此。则丰年多取。必无怨苦之言。凶年减税。方知宽恤之恩。岂非上下相资。而国与民两便乎。夫小民无远虑。若遇丰年。收谷稍多。则未必爱惜
品等数之一定而不变者然。丰年亦然。凶年亦然。敬差官踏验时。亦未尝问及于此而有所低昂。故虽厥数不多。而逢凶则乃为其邑之痼弊矣。地部既不明九等之制。故各邑。亦不留意于是。不择禾稼之丰啬。为之等第。而收税之时。混同加捧。名之曰大同中。薄田残苗。灾伤居半。而亦有加捧之税。岂非无据之甚者乎。今欲适宜收税。只当申明九等之法而已。如庆尚,全罗道土地肥饶之处。丰年则皆用上等。中丰则用中等。他馀道。亦观地之肥瘠。岁之丰凶。递为升降。若逢大凶。则皆用下等。给陈给灾。无所吝惜。若仓储有裕。则或半减全减。固无不可矣。夫税法下下第九等。一结出米四斗。自此以上。每升一等。则各加二斗。至于第一等。二十斗而止。若自下下而升下上。则厥数倍之。自此以上。递加一等而升之。则亦皆倍之。以今下下之税。而升之下上。则税入已倍于前。升之中中。则加二倍矣。以下下收税之时。若无陈灾。则能支一年之用。况加一二倍。则岂无馀储。足以备凶年之用乎。民知其如此。则丰年多取。必无怨苦之言。凶年减税。方知宽恤之恩。岂非上下相资。而国与民两便乎。夫小民无远虑。若遇丰年。收谷稍多。则未必爱惜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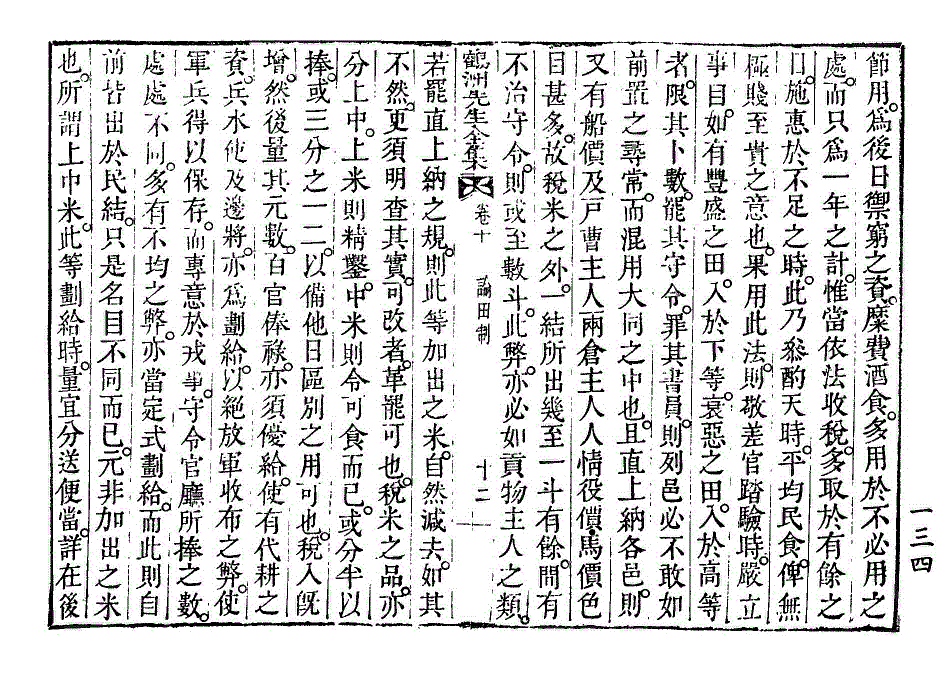 节用。为后日御穷之资。糜费酒食。多用于不必用之处。而只为一年之计。惟当依法收税。多取于有馀之日。施惠于不足之时。此乃参酌天时。平均民食。俾无极贱至贵之意也。果用此法。则敬差官踏验时。严立事目。如有丰盛之田。入于下等。衰恶之田。入于高等者。限其卜数。罢其守令。罪其书员。则列邑必不敢如前置之寻常。而混用大同之中也。且直上纳各邑。则又有船价及户曹主人两仓主人人情役价,马价色目甚多。故税米之外。一结所出几至一斗有馀。间有不治守令。则或至数斗。此弊。亦必如贡物主人之类。若罢直上纳之规。则此等加出之米。自然减去。如其不然。更须明查其实。可改者。革罢可也。税米之品。亦分上中。上米则精凿。中米则令可食而已。或分半以捧。或三分之一二。以备他日区别之用可也。税入既增。然后量其元数。百官俸禄。亦须优给。使有代耕之资。兵水使及边将。亦为划给。以绝放军收布之弊。使军兵得以保存。而专意于戎事。守令官厅所捧之数。处处不同。多有不均之弊。亦当定式划给。而此则自前皆出于民结。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元非加出之米也。所谓上中米。此等划给时。量宜分送便当。详在后
节用。为后日御穷之资。糜费酒食。多用于不必用之处。而只为一年之计。惟当依法收税。多取于有馀之日。施惠于不足之时。此乃参酌天时。平均民食。俾无极贱至贵之意也。果用此法。则敬差官踏验时。严立事目。如有丰盛之田。入于下等。衰恶之田。入于高等者。限其卜数。罢其守令。罪其书员。则列邑必不敢如前置之寻常。而混用大同之中也。且直上纳各邑。则又有船价及户曹主人两仓主人人情役价,马价色目甚多。故税米之外。一结所出几至一斗有馀。间有不治守令。则或至数斗。此弊。亦必如贡物主人之类。若罢直上纳之规。则此等加出之米。自然减去。如其不然。更须明查其实。可改者。革罢可也。税米之品。亦分上中。上米则精凿。中米则令可食而已。或分半以捧。或三分之一二。以备他日区别之用可也。税入既增。然后量其元数。百官俸禄。亦须优给。使有代耕之资。兵水使及边将。亦为划给。以绝放军收布之弊。使军兵得以保存。而专意于戎事。守令官厅所捧之数。处处不同。多有不均之弊。亦当定式划给。而此则自前皆出于民结。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元非加出之米也。所谓上中米。此等划给时。量宜分送便当。详在后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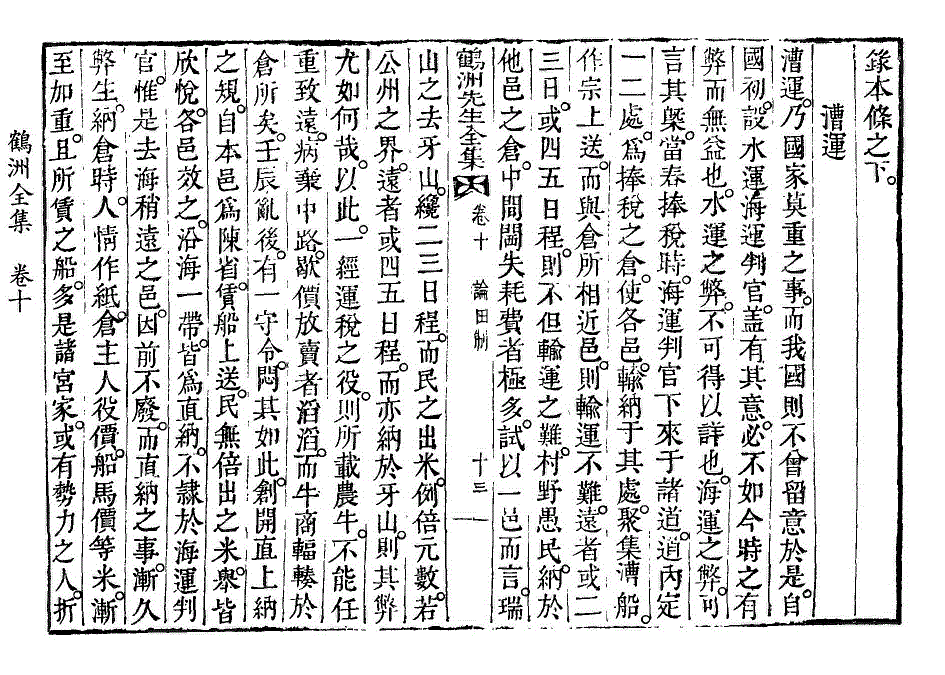 录本条之下。
录本条之下。漕运
漕运。乃国家莫重之事。而我国则不曾留意于是。自国初。设水运,海运判官。盖有其意。必不如今时之有弊而无益也。水运之弊。不可得以详也。海运之弊。可言其槩。当春捧税时。海运判官下来于诸道。道内定一二处。为捧税之仓。使各邑。输纳于其处。聚集漕船。作宗上送。而与仓所相近邑。则输运不难。远者或二三日。或四五日程。则不但输运之难。村野愚民。纳于他邑之仓。中间閪失耗费者极多。试以一邑而言。瑞山之去牙山。才二三日程。而民之出米。例倍元数。若公州之界。远者或四五日程。而亦纳于牙山。则其弊尤如何哉。以此。一经运税之役。则所载农牛。不能任重致远。病弃中路。歇价放卖者滔滔。而牛商辐辏于仓所矣。壬辰乱后。有一守令。闷其如此。创开直上纳之规。自本邑为陈省。赁船上送。民无倍出之米。举皆欣悦。各邑效之。沿海一带。皆为直纳。不隶于海运判官。惟是去海稍远之邑。因前不废。而直纳之事。渐久弊生。纳仓时。人情作纸。仓主人役价。船马价等米。渐至加重。且所赁之船。多是诸宫家。或有势力之人。折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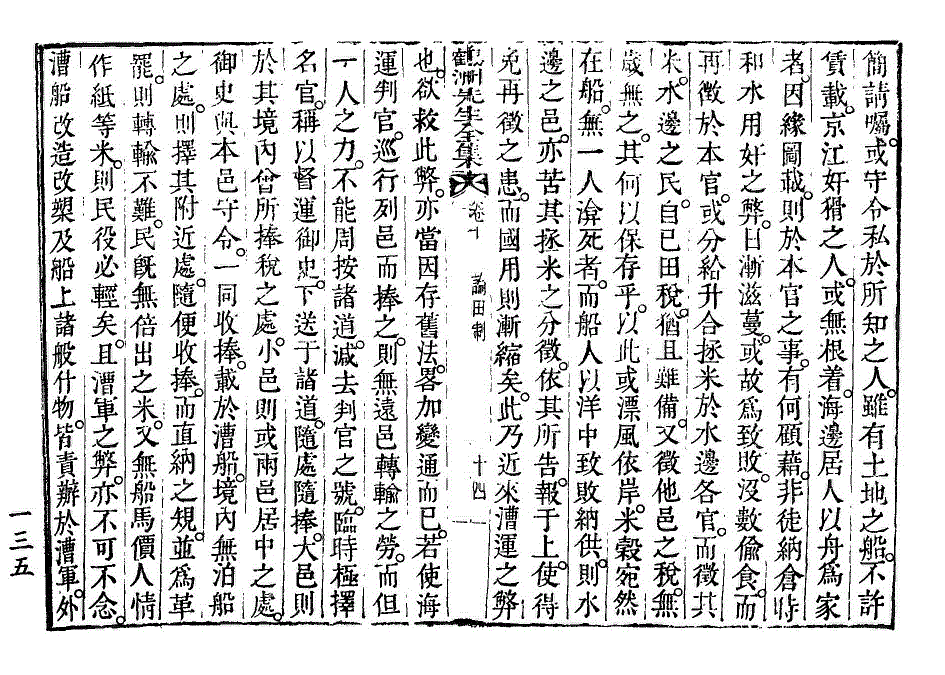 简请嘱。或守令私于所知之人。虽有土地之船。不许赁载。京江奸猾之人。或无根着。海边居人以舟为家者。因缘图载。则于本官之事。有何顾藉。非徒纳仓时和水用奸之弊。日渐滋蔓。或故为致败。没数偷食。而再徵于本官。或分给升合拯米于水边各官。而徵其米。水边之民。自己田税。犹且难备。又徵他邑之税。无岁无之。其何以保存乎。以此或漂风依岸。米谷宛然在船。无一人渰死者。而船人以洋中致败纳供。则水边之邑。亦苦其拯米之分徵。依其所告。报于上。使得免再徵之患。而国用则渐缩矣。此乃近来漕运之弊也。欲救此弊。亦当因存旧法。略加变通而已。若使海运判官。巡行列邑而捧之。则无远邑转输之劳。而但一人之力。不能周按诸道。减去判官之号。临时极择名官。称以督运御史。下送于诸道。随处随捧。大邑则于其境内曾所捧税之处。小邑则或两邑居中之处。御史与本邑守令。一同收捧。载于漕船。境内无泊船之处。则择其附近处。随便收捧。而直纳之规。并为革罢。则转输不难。民既无倍出之米。又无船马价人情作纸等米。则民役必轻矣。且漕军之弊。亦不可不念。漕船改造改槊及船上诸般什物。皆责办于漕军。外
简请嘱。或守令私于所知之人。虽有土地之船。不许赁载。京江奸猾之人。或无根着。海边居人以舟为家者。因缘图载。则于本官之事。有何顾藉。非徒纳仓时和水用奸之弊。日渐滋蔓。或故为致败。没数偷食。而再徵于本官。或分给升合拯米于水边各官。而徵其米。水边之民。自己田税。犹且难备。又徵他邑之税。无岁无之。其何以保存乎。以此或漂风依岸。米谷宛然在船。无一人渰死者。而船人以洋中致败纳供。则水边之邑。亦苦其拯米之分徵。依其所告。报于上。使得免再徵之患。而国用则渐缩矣。此乃近来漕运之弊也。欲救此弊。亦当因存旧法。略加变通而已。若使海运判官。巡行列邑而捧之。则无远邑转输之劳。而但一人之力。不能周按诸道。减去判官之号。临时极择名官。称以督运御史。下送于诸道。随处随捧。大邑则于其境内曾所捧税之处。小邑则或两邑居中之处。御史与本邑守令。一同收捧。载于漕船。境内无泊船之处。则择其附近处。随便收捧。而直纳之规。并为革罢。则转输不难。民既无倍出之米。又无船马价人情作纸等米。则民役必轻矣。且漕军之弊。亦不可不念。漕船改造改槊及船上诸般什物。皆责办于漕军。外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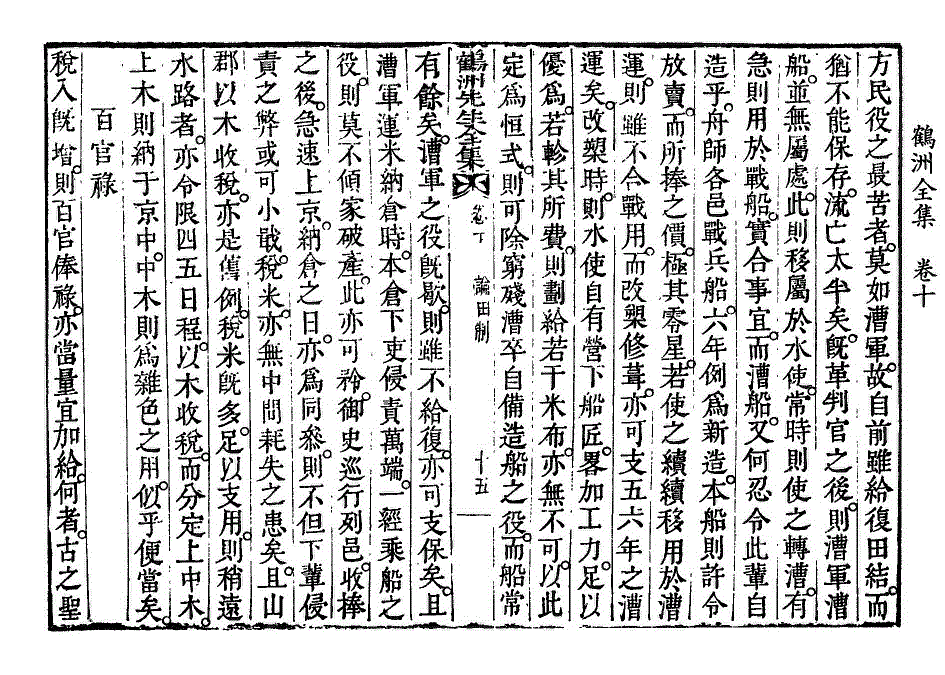 方民役之最苦者。莫如漕军。故自前虽给复田结。而犹不能保存。流亡太半矣。既革判官之后。则漕军漕船。并无属处。此则移属于水使。常时则使之转漕。有急则用于战船。实合事宜。而漕船。又何忍令此辈自造乎。舟师各邑战兵船。六年例为新造。本船则许令放卖。而所捧之价。极其零星。若使之续续移用于漕运。则虽不合战用。而改槊修葺。亦可支五六年之漕运矣。改槊时。则水使自有营下船匠。略加工力。足以优为。若轸其所费。则划给若干米布。亦无不可。以此定为恒式。则可除穷残漕卒自备造船之役。而船常有馀矣。漕军之役既歇。则虽不给复。亦可支保矣。且漕军运米纳仓时。本仓下吏侵责万端。一经乘船之役。则莫不倾家破产。此亦可矜。御史巡行列邑。收捧之后。急速上京。纳仓之日。亦为同参。则不但下辈侵责之弊或可小戢。税米。亦无中间耗失之患矣。且山郡以木收税。亦是旧例。税米既多。足以支用。则稍远水路者。亦令限四五日程。以木收税。而分定上中木。上木则纳于京中。中木则为杂色之用。似乎便当矣。
方民役之最苦者。莫如漕军。故自前虽给复田结。而犹不能保存。流亡太半矣。既革判官之后。则漕军漕船。并无属处。此则移属于水使。常时则使之转漕。有急则用于战船。实合事宜。而漕船。又何忍令此辈自造乎。舟师各邑战兵船。六年例为新造。本船则许令放卖。而所捧之价。极其零星。若使之续续移用于漕运。则虽不合战用。而改槊修葺。亦可支五六年之漕运矣。改槊时。则水使自有营下船匠。略加工力。足以优为。若轸其所费。则划给若干米布。亦无不可。以此定为恒式。则可除穷残漕卒自备造船之役。而船常有馀矣。漕军之役既歇。则虽不给复。亦可支保矣。且漕军运米纳仓时。本仓下吏侵责万端。一经乘船之役。则莫不倾家破产。此亦可矜。御史巡行列邑。收捧之后。急速上京。纳仓之日。亦为同参。则不但下辈侵责之弊或可小戢。税米。亦无中间耗失之患矣。且山郡以木收税。亦是旧例。税米既多。足以支用。则稍远水路者。亦令限四五日程。以木收税。而分定上中木。上木则纳于京中。中木则为杂色之用。似乎便当矣。百官禄
税入既增。则百官俸禄。亦当量宜加给。何者。古之圣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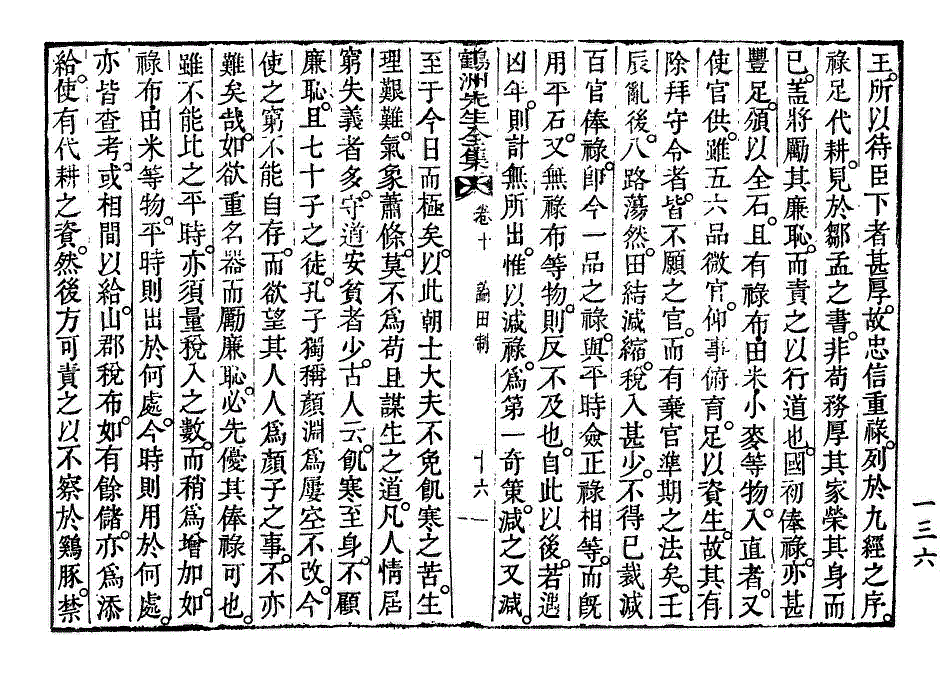 王。所以待臣下者甚厚。故忠信重禄。列于九经之序。禄足代耕。见于邹孟之书。非苟务厚其家荣其身而已。盖将励其廉耻。而责之以行道也。国初俸禄。亦甚丰足。颁以全石。且有禄布,田米,小麦等物。入直者。又使官供。虽五六品微官。仰事俯育。足以资生。故其有除拜守令者。皆不愿之官。而有弃官准期之法矣。壬辰乱后。八路荡然。田结减缩。税入甚少。不得已裁减百官俸禄。即今一品之禄。与平时佥正禄相等。而既用平石。又无禄布等物。则反不及也。自此以后。若遇凶年。则计无所出。惟以减禄。为第一奇策。减之又减。至于今日而极矣。以此朝士大夫不免饥寒之苦。生理艰难。气象萧条。莫不为苟且谋生之道。凡人情居穷失义者多。守道安贫者少。古人云。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且七十子之徒。孔子独称颜渊为屡空不改。今使之穷不能自存。而欲望其人人为颜子之事。不亦难矣哉。如欲重名器而励廉耻。必先优其俸禄可也。虽不能比之平时。亦须量税入之数。而稍为增加。如禄布,田米等物。平时则出于何处。今时则用于何处。亦皆查考。或相间以给。山郡税布。如有馀储。亦为添给。使有代耕之资。然后方可责之以不察于鸡豚。禁
王。所以待臣下者甚厚。故忠信重禄。列于九经之序。禄足代耕。见于邹孟之书。非苟务厚其家荣其身而已。盖将励其廉耻。而责之以行道也。国初俸禄。亦甚丰足。颁以全石。且有禄布,田米,小麦等物。入直者。又使官供。虽五六品微官。仰事俯育。足以资生。故其有除拜守令者。皆不愿之官。而有弃官准期之法矣。壬辰乱后。八路荡然。田结减缩。税入甚少。不得已裁减百官俸禄。即今一品之禄。与平时佥正禄相等。而既用平石。又无禄布等物。则反不及也。自此以后。若遇凶年。则计无所出。惟以减禄。为第一奇策。减之又减。至于今日而极矣。以此朝士大夫不免饥寒之苦。生理艰难。气象萧条。莫不为苟且谋生之道。凡人情居穷失义者多。守道安贫者少。古人云。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且七十子之徒。孔子独称颜渊为屡空不改。今使之穷不能自存。而欲望其人人为颜子之事。不亦难矣哉。如欲重名器而励廉耻。必先优其俸禄可也。虽不能比之平时。亦须量税入之数。而稍为增加。如禄布,田米等物。平时则出于何处。今时则用于何处。亦皆查考。或相间以给。山郡税布。如有馀储。亦为添给。使有代耕之资。然后方可责之以不察于鸡豚。禁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7H 页
 园丁之卖菜也。
园丁之卖菜也。守令禄
我国守令官俸之米。颇甚不均。国初所定衙禄之田。似为官俸。而其数不多。大邑不过数十石。小邑则仅十数石。以此不能支用。故各邑皆有官厅所捧之米。而元无定式。诸道不同。每邑异规。大邑则或至数千石。小邑则才百馀石。或未满百石。湖南则所捧极多。小邑所捧。比岭南大邑。不啻倍蓰。岭南则所捧极少。大邑所捧。比湖南小邑或不及十分之二三。同是一国之郡邑。而俸禄有多寡之悬殊。既非经国之道。而民之出米。亦因此有苦歇不均之弊。此亦不可不变通者也。外官俸禄。不可以京职为率。然亦当依其品秩高下。邑之大小。略为参酌以定。如汉之所谓二千石,六百石可也。即今京官六品之禄。每等六石。合一年计之。则二十四石。外官则或加三四倍。至于三四品亦然。而使客支待。则亦为参酌。或别给四五十石。如四牧监司留住之处。加给一二倍。而此亦不为别捧。使之皆出于田税之中。御史收捧后。以上中米。分半划给。俾无高重滥捧之弊。此后或有如前捧一升之米者。并绳以赃污重律。则守令不敢科外滥徵。各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7L 页
 邑之捧。莫不平均齐整。有一定之式。而民役无不均之弊矣。
邑之捧。莫不平均齐整。有一定之式。而民役无不均之弊矣。阃帅边将禄
阃帅,边将。亦为御敌而设。未有给俸区处之事。使之自食于军卒。已是国初制法。未为详尽。而流来之弊难以尽言。当初则必使兵,水使。分兵训阅于营下。其中有自愿纳粮者。除若干名。使之备纳。以为供顿之资。而其馀则使之入番矣。此路一开。其弊滋蔓。至于今日。则无一人入番者。没数放军收布。而升细尺长。年增月加。且营中日用杂物。亦皆分定于军兵。而称以油军,蜜军,果军,铁军。色目无穷。而所定之数。十倍于市直。军兵一经此役。则财产竭尽。役重如此。故不胜其苦。逃亡者多而侵及邻族。邻族逃亡。则侵及于邻之邻族之族。而齐民无不病矣。此无他。使之放军收布。而不为之定制也。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谁救。滥觞之患。必至之势也。又朝廷。亦知兵,水使有此物力。故敕使时卜定虎豹皮,鹿皮,水獭皮。其他杂物。厥种甚多。及别设都监。有不时之役。则亦多定木。同故兵,水使以为执言之地。而尤无所忌惮。是亦诲盗而已也。既无俸入。而使之自食军兵。则虽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8H 页
 使诸葛亮。为今之兵,水使。亦不过如此。况今之债帅不念国事。只事肥己者乎。是亦相率而食人而已也。呜呼。不幸遇凶年饥馑。民有人相食者。仁人君子。犹且恻隐惊惕。无以为心。况作法制。使之食人而晏然于心。不思所以变通之路乎。若不变通。则国家所恃为卫国之具。终至于无一人保存。而国不为国矣。欲救此弊。亦当以税米。分等划给。而兵使则或给五六百石。水使则给四五百石。佥万户权管。亦须量宜分给。御史收捧后。以上中米。分半划给。则亦无滥捧之弊矣。然后军兵则一意训鍊。而如有如前侵责者。并以军法从事。则军役顿歇。必无流亡。且有精鍊之实。而缓急有所恃矣。
使诸葛亮。为今之兵,水使。亦不过如此。况今之债帅不念国事。只事肥己者乎。是亦相率而食人而已也。呜呼。不幸遇凶年饥馑。民有人相食者。仁人君子。犹且恻隐惊惕。无以为心。况作法制。使之食人而晏然于心。不思所以变通之路乎。若不变通。则国家所恃为卫国之具。终至于无一人保存。而国不为国矣。欲救此弊。亦当以税米。分等划给。而兵使则或给五六百石。水使则给四五百石。佥万户权管。亦须量宜分给。御史收捧后。以上中米。分半划给。则亦无滥捧之弊矣。然后军兵则一意训鍊。而如有如前侵责者。并以军法从事。则军役顿歇。必无流亡。且有精鍊之实。而缓急有所恃矣。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论兵制(九条)
总论
我国兵制之无形。未知自国初而然耶。若壬辰以前。则反不如今日之尚有数件名目也。何者。今之都监三手。外方束伍军。皆创设于壬辰乱后。御营军。又 反正后所募之兵也。平时则只有上番诸色军及步兵。外方各营新选骑,步兵,水军。而考诸大典。则上番之军。厥数不多。而又不为制敌出战之用。除直守阙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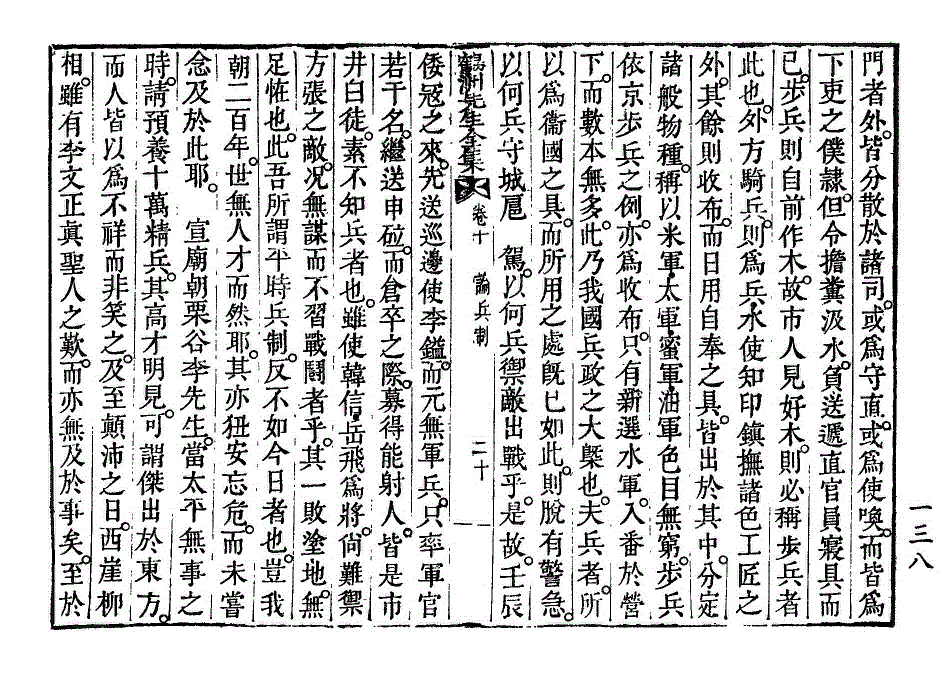 门者外。皆分散于诸司。或为守直。或为使唤。而皆为下吏之仆隶。但令担粪汲水。负送递直官员寝具而已。步兵则自前作木。故市人见好木。则必称步兵者此也。外方骑兵。则为兵,水使知印镇抚诸色工匠之外。其馀则收布。而日用自奉之具。皆出于其中。分定诸般物种。称以米军,太军,蜜军,油军色目无穷。步兵依京步兵之例。亦为收布。只有新选水军。入番于营下。而数本无多。此乃我国兵政之大槩也。夫兵者。所以为卫国之具。而所用之处既已如此。则脱有警急。以何兵守城扈 驾。以何兵御敌出战乎。是故。壬辰倭寇之来。先送巡边使李镒。而元无军兵。只率军官若干名。继送申砬。而仓卒之际。募得能射人。皆是市井白徒。素不知兵者也。虽使韩信,岳飞为将。尚难御方张之敌。况无谋而不习战斗者乎。其一败涂地。无足怪也。此吾所谓平时兵制。反不如今日者也。岂我朝二百年。世无人才而然耶。其亦狃安忘危。而未尝念及于此耶。 宣庙朝栗谷李先生。当太平无事之时。请预养十万精兵。其高才明见。可谓杰出于东方。而人皆以为不祥而非笑之。及至颠沛之日。西崖柳相。虽有李文正真圣人之叹。而亦无及于事矣。至于
门者外。皆分散于诸司。或为守直。或为使唤。而皆为下吏之仆隶。但令担粪汲水。负送递直官员寝具而已。步兵则自前作木。故市人见好木。则必称步兵者此也。外方骑兵。则为兵,水使知印镇抚诸色工匠之外。其馀则收布。而日用自奉之具。皆出于其中。分定诸般物种。称以米军,太军,蜜军,油军色目无穷。步兵依京步兵之例。亦为收布。只有新选水军。入番于营下。而数本无多。此乃我国兵政之大槩也。夫兵者。所以为卫国之具。而所用之处既已如此。则脱有警急。以何兵守城扈 驾。以何兵御敌出战乎。是故。壬辰倭寇之来。先送巡边使李镒。而元无军兵。只率军官若干名。继送申砬。而仓卒之际。募得能射人。皆是市井白徒。素不知兵者也。虽使韩信,岳飞为将。尚难御方张之敌。况无谋而不习战斗者乎。其一败涂地。无足怪也。此吾所谓平时兵制。反不如今日者也。岂我朝二百年。世无人才而然耶。其亦狃安忘危。而未尝念及于此耶。 宣庙朝栗谷李先生。当太平无事之时。请预养十万精兵。其高才明见。可谓杰出于东方。而人皆以为不祥而非笑之。及至颠沛之日。西崖柳相。虽有李文正真圣人之叹。而亦无及于事矣。至于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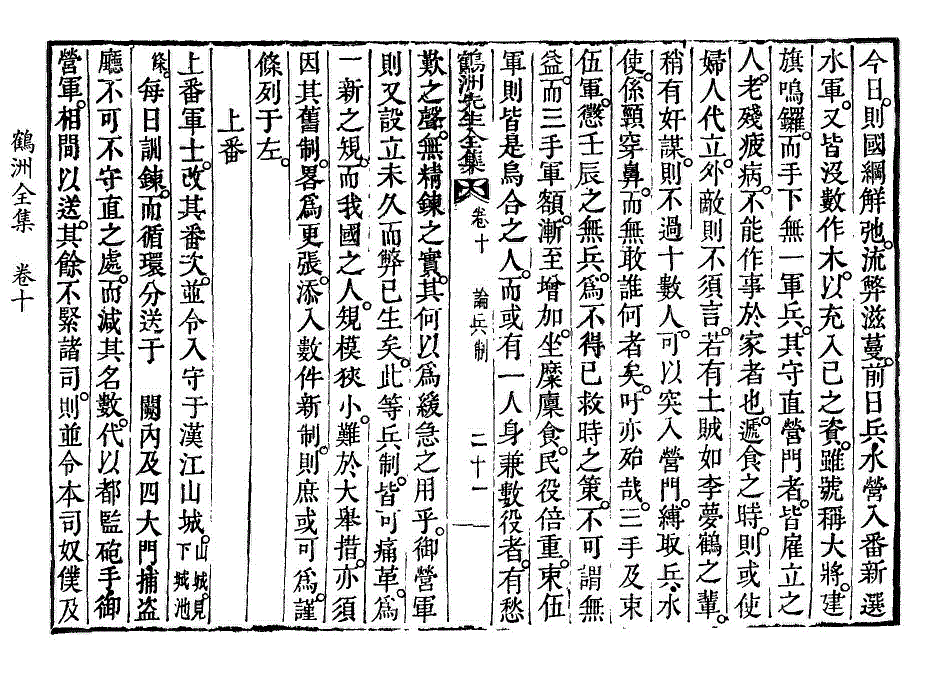 今日。则国纲解弛。流弊滋蔓。前日兵,水营入番新选水军。又皆没数作木。以充入己之资。虽号称大将。建旗鸣锣。而手下无一军兵。其守直营门者。皆雇立之人。老残疲病。不能作事于家者也。递食之时。则或使妇人代立。外敌则不须言。若有土贼如李梦鹤之辈。稍有奸谋。则不过十数人。可以突入营门。缚取兵,水使。系颈穿鼻。而无敢谁何者矣。吁亦殆哉。三手及束伍军。惩壬辰之无兵。为不得已救时之策。不可谓无益。而三手军额。渐至增加。坐糜廪食。民役倍重。束伍军则皆是乌合之人。而或有一人身兼数役者。有愁叹之声。无精鍊之实。其何以为缓急之用乎。御营军则又设立未久而弊已生矣。此等兵制。皆可痛革。为一新之规。而我国之人。规模狭小。难于大举措。亦须因其旧制。略为更张。添入数件新制。则庶或可为。谨条列于左。
今日。则国纲解弛。流弊滋蔓。前日兵,水营入番新选水军。又皆没数作木。以充入己之资。虽号称大将。建旗鸣锣。而手下无一军兵。其守直营门者。皆雇立之人。老残疲病。不能作事于家者也。递食之时。则或使妇人代立。外敌则不须言。若有土贼如李梦鹤之辈。稍有奸谋。则不过十数人。可以突入营门。缚取兵,水使。系颈穿鼻。而无敢谁何者矣。吁亦殆哉。三手及束伍军。惩壬辰之无兵。为不得已救时之策。不可谓无益。而三手军额。渐至增加。坐糜廪食。民役倍重。束伍军则皆是乌合之人。而或有一人身兼数役者。有愁叹之声。无精鍊之实。其何以为缓急之用乎。御营军则又设立未久而弊已生矣。此等兵制。皆可痛革。为一新之规。而我国之人。规模狭小。难于大举措。亦须因其旧制。略为更张。添入数件新制。则庶或可为。谨条列于左。上番
上番军士。改其番次。并令入守于汉江山城。(山城。见下城池条。)每日训鍊。而循环分送于 阙内及四大门,捕盗厅不可不守直之处。而减其名数。代以都监炮手,御营军。相间以送。其馀不紧诸司。则并令本司奴仆及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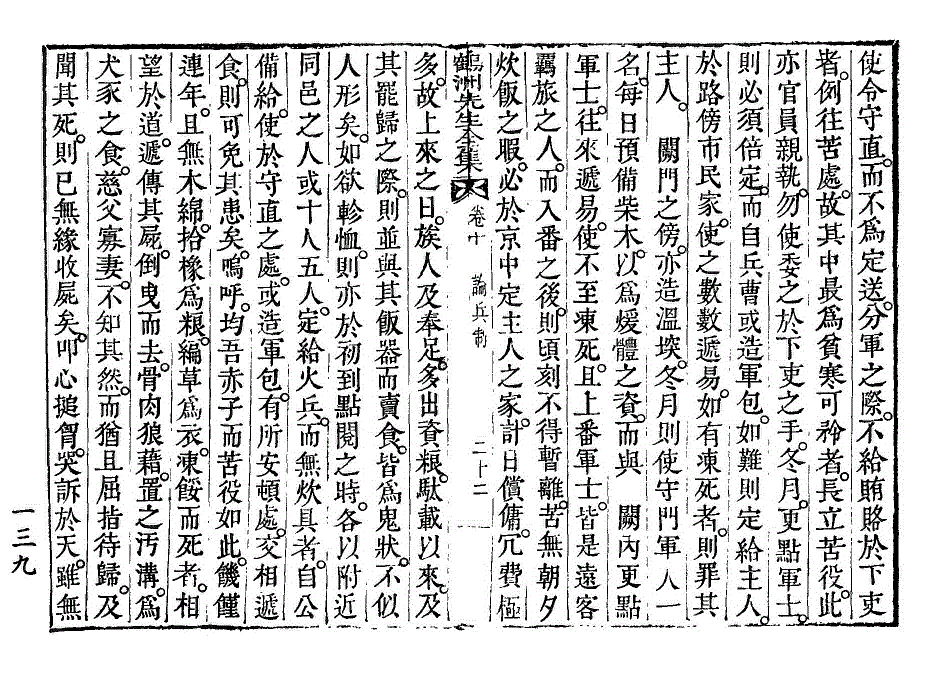 使令守直。而不为定送。分军之际。不给贿赂于下吏者。例往苦处。故其中最为贫寒可矜者。长立苦役。此亦官员亲执。勿使委之于下吏之手。冬月。更点军士。则必须倍定。而自兵曹或造军包。如难则定给主人。于路傍市民家。使之数数递易。如有冻死者。则罪其主人。 阙门之傍。亦造温突。冬月则使守门军人一名。每日预备柴木。以为煖体之资。而与 阙内更点军士。往来递易。使不至冻死。且上番军士。皆是远客羁旅之人。而入番之后。则顷刻不得暂离。苦无朝夕炊饭之暇。必于京中定主人之家。计日偿佣。冗费极多。故上来之日。族人及奉足。多出资粮。驮载以来。及其罢归之际。则并与其饭器而卖食。皆为鬼状。不似人形矣。如欲轸恤。则亦于初到点阅之时。各以附近同邑之人或十人五人。定给火兵。而无炊具者。自公备给。使于守直之处。或造军包。有所安顿处。交相递食。则可免其患矣。呜呼。均吾赤子而苦役如此。饥馑连年。且无木绵。拾橡为粮。编草为衣。冻馁而死者。相望于道。递传其尸。倒曳而去。骨肉狼藉。置之污沟。为犬豕之食。慈父寡妻。不知其然。而犹且屈指待归。及闻其死。则已无缘收尸矣。叩心搥胸。哭诉于天。虽无
使令守直。而不为定送。分军之际。不给贿赂于下吏者。例往苦处。故其中最为贫寒可矜者。长立苦役。此亦官员亲执。勿使委之于下吏之手。冬月。更点军士。则必须倍定。而自兵曹或造军包。如难则定给主人。于路傍市民家。使之数数递易。如有冻死者。则罪其主人。 阙门之傍。亦造温突。冬月则使守门军人一名。每日预备柴木。以为煖体之资。而与 阙内更点军士。往来递易。使不至冻死。且上番军士。皆是远客羁旅之人。而入番之后。则顷刻不得暂离。苦无朝夕炊饭之暇。必于京中定主人之家。计日偿佣。冗费极多。故上来之日。族人及奉足。多出资粮。驮载以来。及其罢归之际。则并与其饭器而卖食。皆为鬼状。不似人形矣。如欲轸恤。则亦于初到点阅之时。各以附近同邑之人或十人五人。定给火兵。而无炊具者。自公备给。使于守直之处。或造军包。有所安顿处。交相递食。则可免其患矣。呜呼。均吾赤子而苦役如此。饥馑连年。且无木绵。拾橡为粮。编草为衣。冻馁而死者。相望于道。递传其尸。倒曳而去。骨肉狼藉。置之污沟。为犬豕之食。慈父寡妻。不知其然。而犹且屈指待归。及闻其死。则已无缘收尸矣。叩心搥胸。哭诉于天。虽无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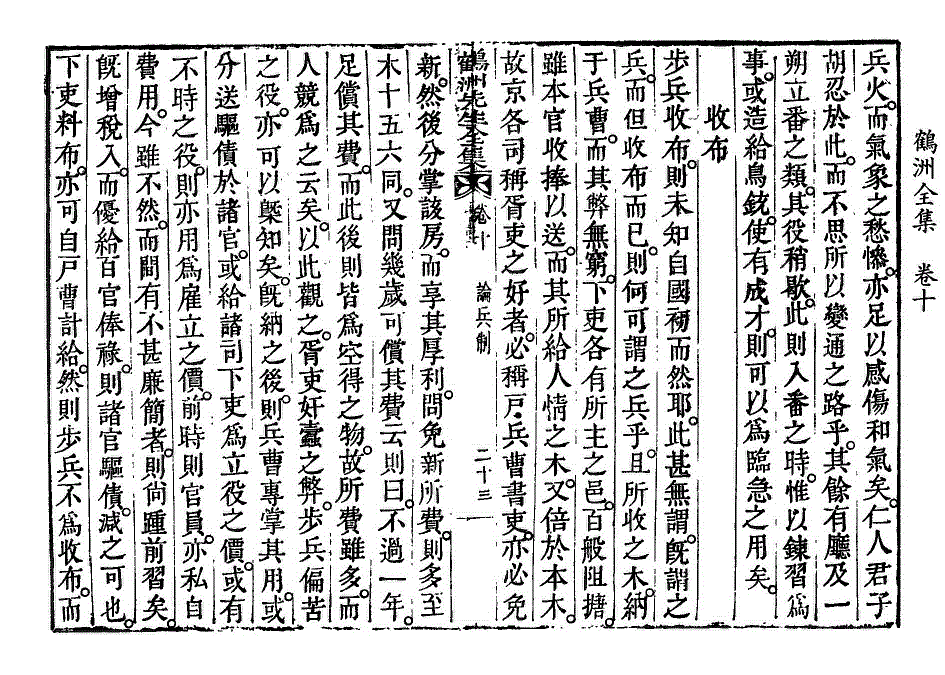 兵火。而气象之愁惨。亦足以感伤和气矣。仁人君子胡忍于此。而不思所以变通之路乎。其馀有厅及一朔立番之类。其役稍歇。此则入番之时。惟以鍊习为事。或造给鸟铳。使有成才。则可以为临急之用矣。
兵火。而气象之愁惨。亦足以感伤和气矣。仁人君子胡忍于此。而不思所以变通之路乎。其馀有厅及一朔立番之类。其役稍歇。此则入番之时。惟以鍊习为事。或造给鸟铳。使有成才。则可以为临急之用矣。收布
步兵收布。则未知自国初而然耶。此甚无谓。既谓之兵。而但收布而已。则何可谓之兵乎。且所收之木。纳于兵曹。而其弊无穷。下吏各有所主之邑。百般阻搪。虽本官收捧以送。而其所给人情之木。又倍于本木。故京各司称胥吏之好者。必称户,兵曹书吏。亦必免新。然后分掌该房。而享其厚利。问免新所费。则多至木十五六同。又问几岁可偿其费云则曰。不过一年。足偿其费。而此后则皆为空得之物。故所费虽多。而人竞为之云矣。以此观之。胥吏奸蠹之弊。步兵偏苦之役。亦可以槩知矣。既纳之后。则兵曹专掌其用。或分送驱债于诸官。或给诸司下吏为立役之价。或有不时之役。则亦用为雇立之价。前时则官员。亦私自费用。今虽不然。而间有不甚廉简者。则尚踵前习矣。既增税入。而优给百官俸禄。则诸官驱债。减之可也。下吏料布。亦可自户曹计给。然则步兵不为收布。而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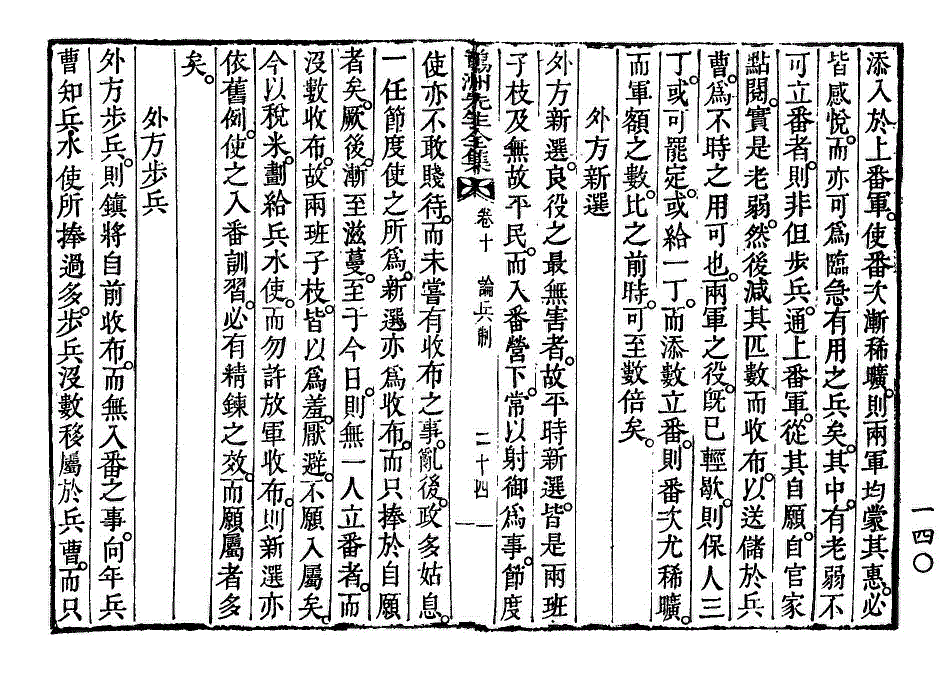 添入于上番军。使番次渐稀旷。则两军均蒙其惠。必皆感悦。而亦可为临急有用之兵矣。其中。有老弱不可立番者。则非但步兵。通上番军。从其自愿。自官家点阅。实是老弱。然后减其匹数而收布。以送储于兵曹。为不时之用可也。两军之役。既已轻歇。则保人三丁。或可罢定。或给一丁。而添数立番。则番次尤稀旷。而军额之数。比之前时。可至数倍矣。
添入于上番军。使番次渐稀旷。则两军均蒙其惠。必皆感悦。而亦可为临急有用之兵矣。其中。有老弱不可立番者。则非但步兵。通上番军。从其自愿。自官家点阅。实是老弱。然后减其匹数而收布。以送储于兵曹。为不时之用可也。两军之役。既已轻歇。则保人三丁。或可罢定。或给一丁。而添数立番。则番次尤稀旷。而军额之数。比之前时。可至数倍矣。外方新选
外方新选。良役之最无害者。故平时新选。皆是两班子枝及无故平民。而入番营下。常以射御为事。节度使亦不敢贱待。而未尝有收布之事。乱后。政多姑息。一任节度使之所为。新选亦为收布。而只捧于自愿者矣。厥后。渐至滋蔓。至于今日。则无一人立番者。而没数收布。故两班子枝。皆以为羞。厌避。不愿入属矣。今以税米。划给兵水使。而勿许放军收布。则新选亦依旧例。使之入番训习。必有精鍊之效。而愿属者多矣。
外方步兵
外方步兵。则镇将自前收布。而无入番之事。向年兵曹知兵,水使所捧过多。步兵没数移属于兵曹。而只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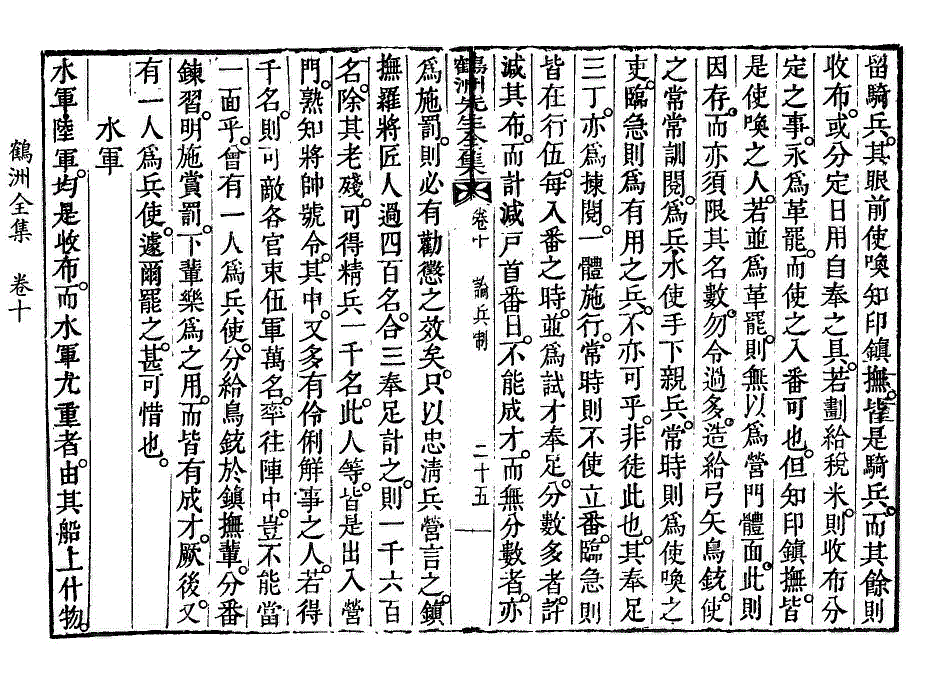 留骑兵。其眼前使唤知印镇抚。皆是骑兵。而其馀则收布。或分定日用自奉之具。若划给税米。则收布分定之事。永为革罢。而使之入番可也。但知印镇抚。皆是使唤之人。若并为革罢。则无以为营门体面。此则因存。而亦须限其名数。勿令过多。造给弓矢鸟铳。使之常常训阅。为兵,水使手下亲兵。常时则为使唤之吏。临急则为有用之兵。不亦可乎。非徒此也。其奉足三丁。亦为拣阅。一体施行。常时则不使立番。临急则皆在行伍。每入番之时。并为试才奉足。分数多者。许减其布。而计减户首番日。不能成才。而无分数者。亦为施罚。则必有劝惩之效矣。只以忠清兵营言之。镇抚罗将匠人过四百名。合三奉足计之。则一千六百名。除其老残。可得精兵一千名。此人等。皆是出入营门。熟知将帅号令。其中。又多有伶俐解事之人。若得千名。则可敌各官束伍军万名。率往阵中。岂不能当一面乎。曾有一人为兵使。分给鸟铳于镇抚辈。分番鍊习。明施赏罚。下辈乐为之用。而皆有成才。厥后。又有一人为兵使。遽尔罢之。甚可惜也。
留骑兵。其眼前使唤知印镇抚。皆是骑兵。而其馀则收布。或分定日用自奉之具。若划给税米。则收布分定之事。永为革罢。而使之入番可也。但知印镇抚。皆是使唤之人。若并为革罢。则无以为营门体面。此则因存。而亦须限其名数。勿令过多。造给弓矢鸟铳。使之常常训阅。为兵,水使手下亲兵。常时则为使唤之吏。临急则为有用之兵。不亦可乎。非徒此也。其奉足三丁。亦为拣阅。一体施行。常时则不使立番。临急则皆在行伍。每入番之时。并为试才奉足。分数多者。许减其布。而计减户首番日。不能成才。而无分数者。亦为施罚。则必有劝惩之效矣。只以忠清兵营言之。镇抚罗将匠人过四百名。合三奉足计之。则一千六百名。除其老残。可得精兵一千名。此人等。皆是出入营门。熟知将帅号令。其中。又多有伶俐解事之人。若得千名。则可敌各官束伍军万名。率往阵中。岂不能当一面乎。曾有一人为兵使。分给鸟铳于镇抚辈。分番鍊习。明施赏罚。下辈乐为之用。而皆有成才。厥后。又有一人为兵使。遽尔罢之。甚可惜也。水军
水军,陆军。均是收布。而水军尤重者。由其船上什物。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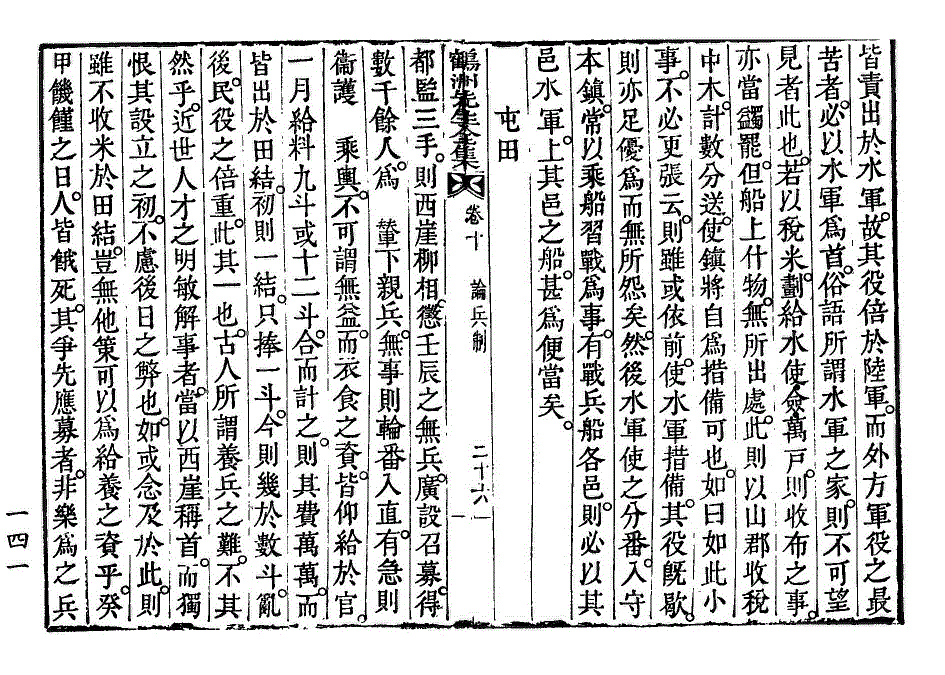 皆责出于水军。故其役倍于陆军。而外方军役之最苦者。必以水军为首。俗语所谓水军之家。则不可望见者此也。若以税米。划给水使,佥,万户。则收布之事。亦当蠲罢。但船上什物。无所出处。此则以山郡收税中木。计数分送。使镇将自为措备可也。如曰如此小事。不必更张云。则虽或依前。使水军措备。其役既歇。则亦足优为而无所怨矣。然后水军使之分番。入守本镇。常以乘船习战为事。有战兵船各邑。则必以其邑水军。上其邑之船。甚为便当矣。
皆责出于水军。故其役倍于陆军。而外方军役之最苦者。必以水军为首。俗语所谓水军之家。则不可望见者此也。若以税米。划给水使,佥,万户。则收布之事。亦当蠲罢。但船上什物。无所出处。此则以山郡收税中木。计数分送。使镇将自为措备可也。如曰如此小事。不必更张云。则虽或依前。使水军措备。其役既歇。则亦足优为而无所怨矣。然后水军使之分番。入守本镇。常以乘船习战为事。有战兵船各邑。则必以其邑水军。上其邑之船。甚为便当矣。屯田
都监三手。则西崖柳相。惩壬辰之无兵。广设召募。得数千馀人。为 辇下亲兵。无事则轮番入直。有急则卫护 乘舆。不可谓无益。而衣食之资。皆仰给于官。一月给料九斗或十二斗。合而计之。则其费万万。而皆出于田结。初则一结。只捧一斗。今则几于数斗。乱后。民役之倍重。此其一也。古人所谓养兵之难。不其然乎。近世人才之明敏解事者。当以西崖称首。而独恨其设立之初。不虑后日之弊也。如或念及于此。则虽不收米于田结。岂无他策可以为给养之资乎。癸甲饥馑之日。人皆饿死。其争先应募者。非乐为之兵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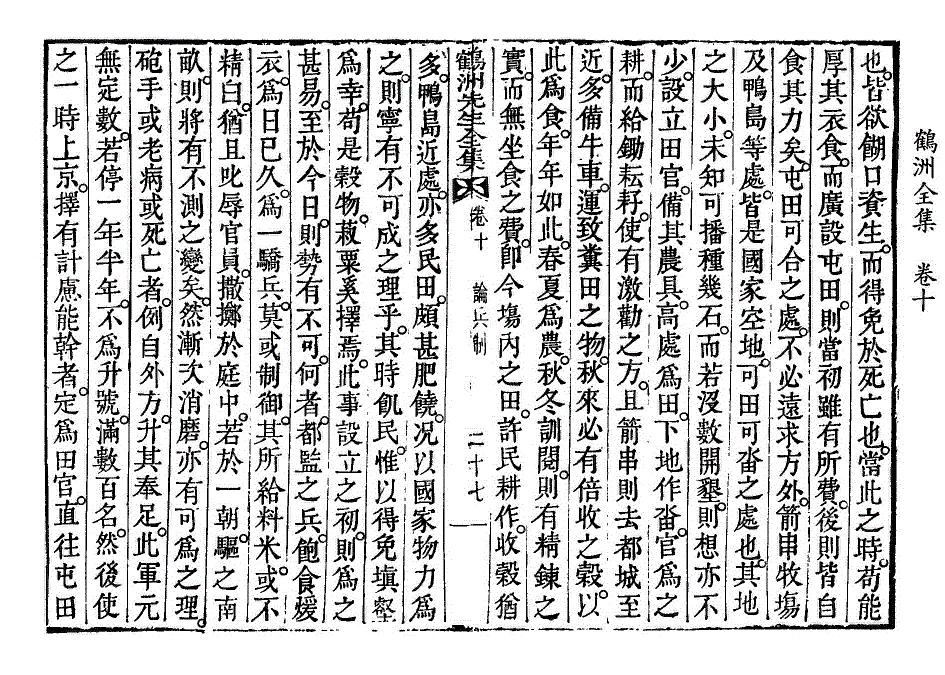 也。皆欲糊口资生。而得免于死亡也。当此之时。苟能厚其衣食。而广设屯田。则当初虽有所费。后则皆自食其力矣。屯田可合之处。不必远求方外。箭串牧场及鸭岛等处。皆是国家空地。可田可畓之处也。其地之大小。未知可播种几石。而若没数开垦。则想亦不少。设立田官。备其农具。高处为田。下地作畓。官为之耕。而给锄耘耔。使有激劝之方。且箭串则去都城至近。多备牛车。运致粪田之物。秋来必有倍收之谷。以此为食。年年如此。春夏为农。秋冬训阅。则有精鍊之实。而无坐食之费。即今场内之田。许民耕作。收谷犹多。鸭岛近处。亦多民田。颇甚肥饶。况以国家物力为之。则宁有不可成之理乎。其时饥民。惟以得免填壑为幸。苟是谷物。菽粟奚择焉。此事设立之初。则为之甚易。至于今日。则势有不可。何者。都监之兵。饱食煖衣。为日已久。为一骄兵。莫或制御。其所给料米。或不精白。犹且叱辱官员。撒掷于庭中。若于一朝。驱之南亩。则将有不测之变矣。然渐次消磨。亦有可为之理。炮手或老病或死亡者。例自外方。升其奉足。此军元无定数。若停一年半年。不为升号。满数百名。然后使之一时上京。择有计虑能干者。定为田官。直往屯田
也。皆欲糊口资生。而得免于死亡也。当此之时。苟能厚其衣食。而广设屯田。则当初虽有所费。后则皆自食其力矣。屯田可合之处。不必远求方外。箭串牧场及鸭岛等处。皆是国家空地。可田可畓之处也。其地之大小。未知可播种几石。而若没数开垦。则想亦不少。设立田官。备其农具。高处为田。下地作畓。官为之耕。而给锄耘耔。使有激劝之方。且箭串则去都城至近。多备牛车。运致粪田之物。秋来必有倍收之谷。以此为食。年年如此。春夏为农。秋冬训阅。则有精鍊之实。而无坐食之费。即今场内之田。许民耕作。收谷犹多。鸭岛近处。亦多民田。颇甚肥饶。况以国家物力为之。则宁有不可成之理乎。其时饥民。惟以得免填壑为幸。苟是谷物。菽粟奚择焉。此事设立之初。则为之甚易。至于今日。则势有不可。何者。都监之兵。饱食煖衣。为日已久。为一骄兵。莫或制御。其所给料米。或不精白。犹且叱辱官员。撒掷于庭中。若于一朝。驱之南亩。则将有不测之变矣。然渐次消磨。亦有可为之理。炮手或老病或死亡者。例自外方。升其奉足。此军元无定数。若停一年半年。不为升号。满数百名。然后使之一时上京。择有计虑能干者。定为田官。直往屯田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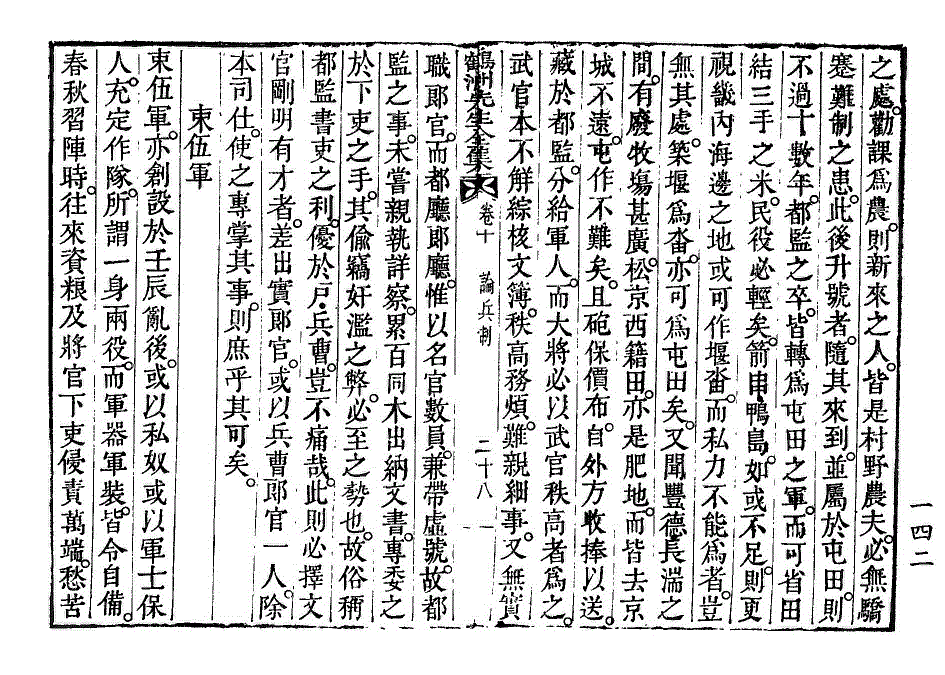 之处。劝课为农。则新来之人。皆是村野农夫。必无骄蹇难制之患。此后升号者。随其来到。并属于屯田。则不过十数年。都监之卒。皆转为屯田之军。而可省田结三手之米。民役必轻矣。箭串,鸭岛。如或不足。则更视畿内海边之地或可作堰畓。而私力不能为者。岂无其处。筑堰为畓。亦可为屯田矣。又闻丰德,长湍之间。有废牧场甚广。松京西籍田。亦是肥地。而皆去京城不远。屯作不难矣。且炮保价布。自外方收捧以送。藏于都监。分给军人。而大将必以武官秩高者为之。武官本不解综核文簿。秩高务烦。难亲细事。又无实职郎官。而都厅郎厅。惟以名官数员。兼带虚号。故都监之事。未尝亲执详察。累百同木出纳文书。专委之于下吏之手。其偷窃奸滥之弊。必至之势也。故俗称都监书吏之利。优于户,兵曹。岂不痛哉。此则必择文官刚明有才者。差出实郎官。或以兵曹郎官一人。除本司仕。使之专掌其事。则庶乎其可矣。
之处。劝课为农。则新来之人。皆是村野农夫。必无骄蹇难制之患。此后升号者。随其来到。并属于屯田。则不过十数年。都监之卒。皆转为屯田之军。而可省田结三手之米。民役必轻矣。箭串,鸭岛。如或不足。则更视畿内海边之地或可作堰畓。而私力不能为者。岂无其处。筑堰为畓。亦可为屯田矣。又闻丰德,长湍之间。有废牧场甚广。松京西籍田。亦是肥地。而皆去京城不远。屯作不难矣。且炮保价布。自外方收捧以送。藏于都监。分给军人。而大将必以武官秩高者为之。武官本不解综核文簿。秩高务烦。难亲细事。又无实职郎官。而都厅郎厅。惟以名官数员。兼带虚号。故都监之事。未尝亲执详察。累百同木出纳文书。专委之于下吏之手。其偷窃奸滥之弊。必至之势也。故俗称都监书吏之利。优于户,兵曹。岂不痛哉。此则必择文官刚明有才者。差出实郎官。或以兵曹郎官一人。除本司仕。使之专掌其事。则庶乎其可矣。束伍军
束伍军。亦创设于壬辰乱后。或以私奴或以军士保人。充定作队。所谓一身两役。而军器军装。皆令自备。春秋习阵时。往来资粮及将官下吏侵责万端。愁苦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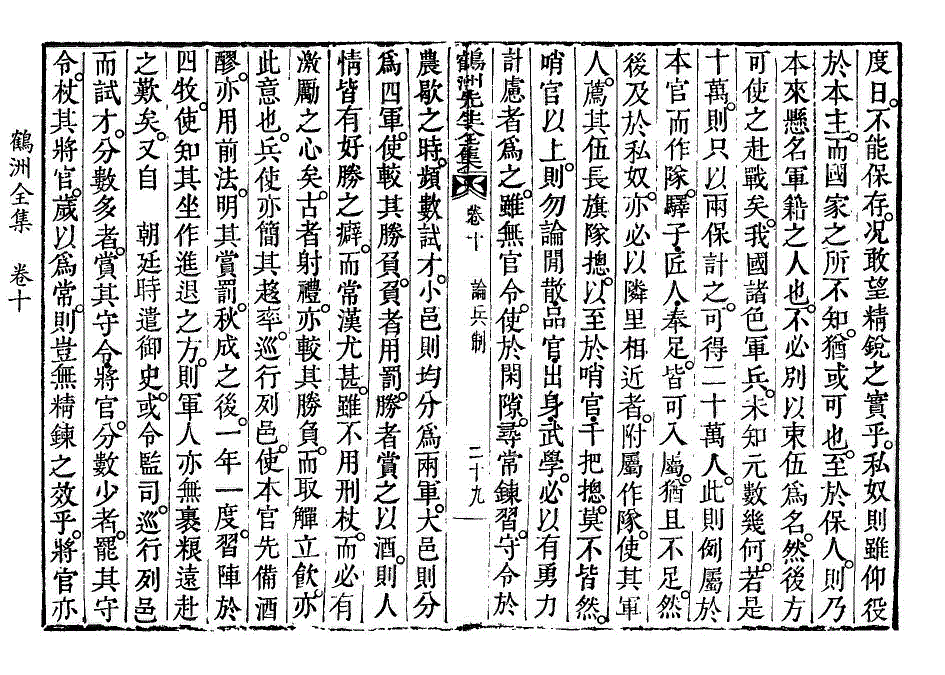 度日。不能保存。况敢望精锐之实乎。私奴则虽仰役于本主。而国家之所不知。犹或可也。至于保人。则乃本来悬名军籍之人也。不必别以束伍为名。然后方可使之赴战矣。我国诸色军兵。未知元数几何。若是十万。则只以两保计之。可得二十万人。此则例属于本官而作队。驿子,匠人,奉足。皆可入属。犹且不足。然后及于私奴。亦必以邻里相近者。附属作队。使其军人。荐其伍长旗队总。以至于哨官,千把总。莫不皆然。哨官以上。则勿论閒散,品官,出身,武学。必以有勇力计虑者为之。虽无官令。使于闲隙。寻常鍊习。守令于农歇之时。频数试才。小邑则均分为两军。大邑则分为四军。使较其胜负。负者用罚。胜者赏之以酒。则人情皆有好胜之癖。而常汉尤甚。虽不用刑杖。而必有激励之心矣。古者射礼。亦较其胜负。而取觯立饮。亦此意也。兵使亦简其趋率。巡行列邑。使本官先备酒醪。亦用前法。明其赏罚。秋成之后。一年一度。习阵于四牧。使知其坐作进退之方。则军人亦无裹粮远赴之叹矣。又自 朝廷时遣御史。或令监司。巡行列邑而试才。分数多者。赏其守令,将官。分数少者。罢其守令。杖其将官。岁以为常。则岂无精鍊之效乎。将官亦
度日。不能保存。况敢望精锐之实乎。私奴则虽仰役于本主。而国家之所不知。犹或可也。至于保人。则乃本来悬名军籍之人也。不必别以束伍为名。然后方可使之赴战矣。我国诸色军兵。未知元数几何。若是十万。则只以两保计之。可得二十万人。此则例属于本官而作队。驿子,匠人,奉足。皆可入属。犹且不足。然后及于私奴。亦必以邻里相近者。附属作队。使其军人。荐其伍长旗队总。以至于哨官,千把总。莫不皆然。哨官以上。则勿论閒散,品官,出身,武学。必以有勇力计虑者为之。虽无官令。使于闲隙。寻常鍊习。守令于农歇之时。频数试才。小邑则均分为两军。大邑则分为四军。使较其胜负。负者用罚。胜者赏之以酒。则人情皆有好胜之癖。而常汉尤甚。虽不用刑杖。而必有激励之心矣。古者射礼。亦较其胜负。而取觯立饮。亦此意也。兵使亦简其趋率。巡行列邑。使本官先备酒醪。亦用前法。明其赏罚。秋成之后。一年一度。习阵于四牧。使知其坐作进退之方。则军人亦无裹粮远赴之叹矣。又自 朝廷时遣御史。或令监司。巡行列邑而试才。分数多者。赏其守令,将官。分数少者。罢其守令。杖其将官。岁以为常。则岂无精鍊之效乎。将官亦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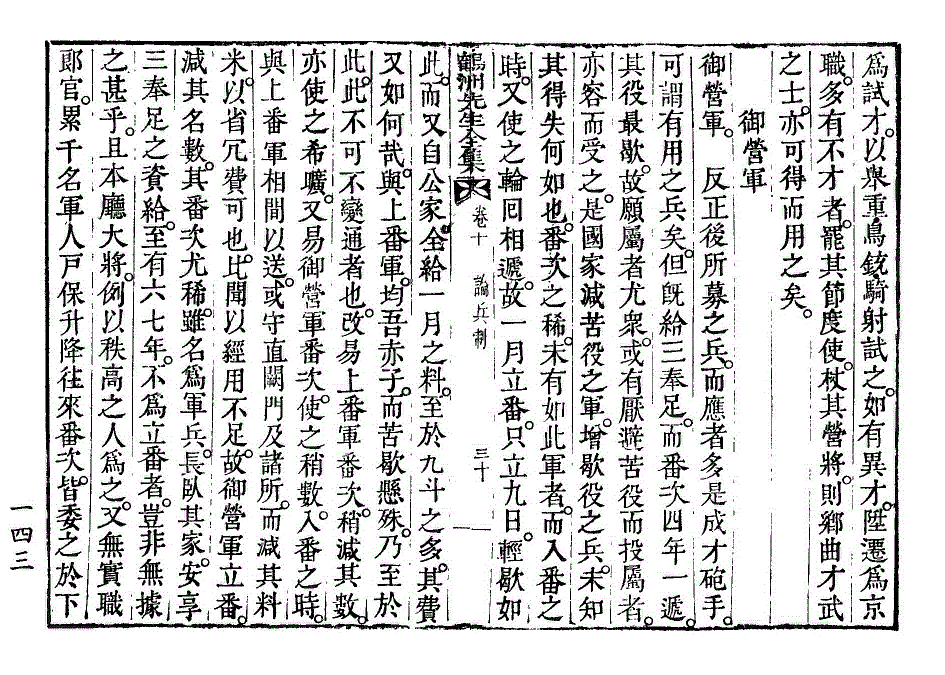 为试才。以举重,鸟铳,骑射试之。如有异才。升迁为京职。多有不才者。罢其节度使。杖其营将。则乡曲才武之士。亦可得而用之矣。
为试才。以举重,鸟铳,骑射试之。如有异才。升迁为京职。多有不才者。罢其节度使。杖其营将。则乡曲才武之士。亦可得而用之矣。御营军
御营军。 反正后所募之兵。而应者多是成才炮手。可谓有用之兵矣。但既给三奉足。而番次四年一递。其役最歇。故愿属者尤众。或有厌避苦役而投属者。亦容而受之。是国家减苦役之军。增歇役之兵。未知其得失何如也。番次之稀。未有如此军者。而入番之时。又使之轮回相递。故一月立番。只立九日。轻歇如此。而又自公家。全给一月之料。至于九斗之多。其费又如何哉。与上番军。均吾赤子。而苦歇悬殊。乃至于此。此不可不变通者也。改易上番军番次。稍减其数。亦使之希旷。又易御营军番次。使之稍数。入番之时。与上番军相间以送。或守直阙门及诸所。而减其料米。以省冗费可也。比闻以经用不足。故御营军立番。减其名数。其番次尤稀。虽名为军兵。长卧其家。安享三奉足之资给。至有六七年。不为立番者。岂非无据之甚乎。且本厅大将。例以秩高之人为之。又无实职郎官。累千名军人户保升降往来番次。皆委之于下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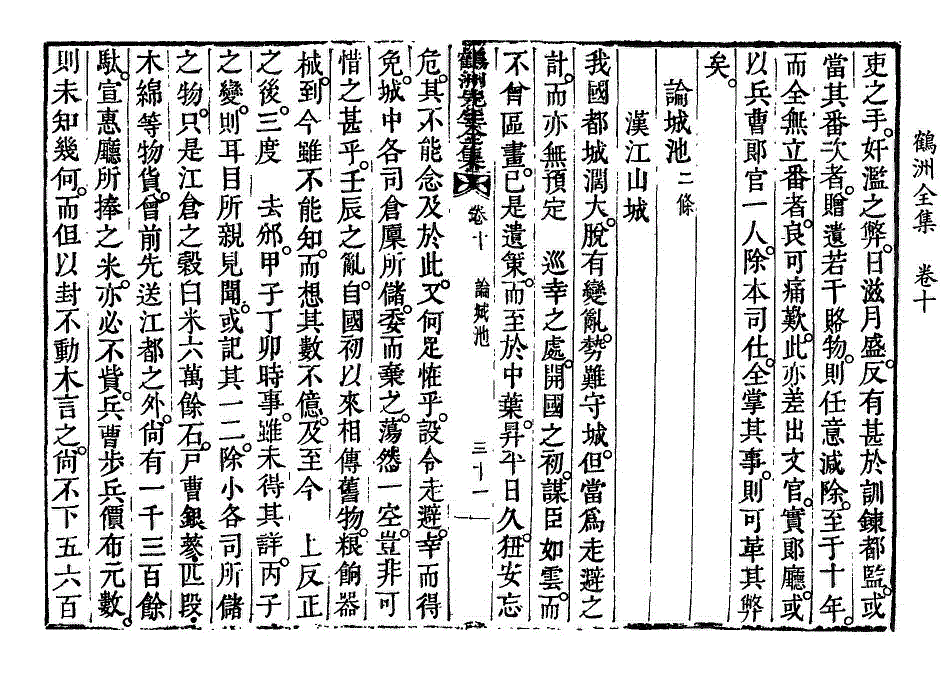 吏之手。奸滥之弊。日滋月盛。反有甚于训鍊都监。或当其番次者。赠遗若干赂物。则任意减除。至于十年。而全无立番者。良可痛叹。此亦差出文官。实郎厅。或以兵曹郎官一人。除本司仕。全掌其事。则可革其弊矣。
吏之手。奸滥之弊。日滋月盛。反有甚于训鍊都监。或当其番次者。赠遗若干赂物。则任意减除。至于十年。而全无立番者。良可痛叹。此亦差出文官。实郎厅。或以兵曹郎官一人。除本司仕。全掌其事。则可革其弊矣。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论城池(二条)
汉江山城
我国都城阔大。脱有变乱。势难守城。但当为走避之计。而亦无预定 巡幸之处。开国之初。谋臣如云。而不曾区画。已是遗策。而至于中叶。升平日久。狃安忘危。其不能念及于此。又何足怪乎。设令走避。幸而得免。城中各司仓廪所储。委而弃之。荡然一空。岂非可惜之甚乎。壬辰之乱。自国初以来相传旧物。粮饷器械。到今虽不能知。而想其数不亿。及至今 上反正之后。三度 去邠。甲子丁卯时事。虽未得其详。丙子之变。则耳目所亲见闻。或记其一二。除小各司所储之物。只是江仓之谷白米六万馀石。户曹银蔘,匹段,木绵等物货。曾前先送江都之外。尚有一千三百馀驮。宣惠厅所捧之米。亦必不赀。兵曹步兵价布元数。则未知几何。而但以封不动木言之。尚不下五六百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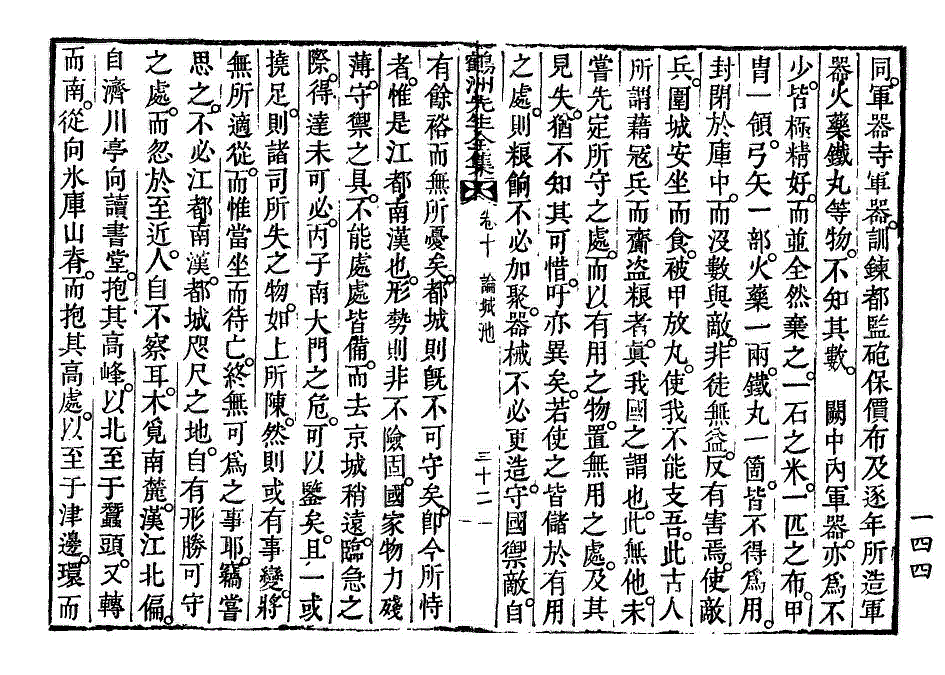 同。军器寺军器。训鍊都监炮保价布及逐年所造军器,火药,铁丸等物。不知其数。 阙中内军器。亦为不少。皆极精好。而并全然弃之。一石之米。一匹之布。甲胄一领。弓矢一部。火药一两。铁丸一个。皆不得为用。封闭于库中。而没数与敌。非徒无益。反有害焉。使敌兵。围城安坐而食。被甲放丸。使我不能支吾。此古人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真我国之谓也。此无他。未尝先定所守之处。而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处。及其见失。犹不知其可惜。吁亦异矣。若使之皆储于有用之处。则粮饷不必加聚。器械不必更造。守国御敌。自有馀裕而无所忧矣。都城则既不可守矣。即今所恃者。惟是江都,南汉也。形势则非不险固。国家物力残薄。守御之具。不能处处皆备。而去京城稍远。临急之际。得达未可必。丙子南大门之危。可以鉴矣。具一或挠足。则诸司所失之物。如上所陈。然则或有事变。将无所适从。而惟当坐而待亡。终无可为之事耶。窃尝思之。不必江都,南汉。都城咫尺之地。自有形胜可守之处。而忽于至近。人自不察耳。木觅南麓。汉江北偏。自济川亭向读书堂。抱其高峰。以北至于蚕头。又转而南。从向冰库山脊。而抱其高处。以至于津边。环而
同。军器寺军器。训鍊都监炮保价布及逐年所造军器,火药,铁丸等物。不知其数。 阙中内军器。亦为不少。皆极精好。而并全然弃之。一石之米。一匹之布。甲胄一领。弓矢一部。火药一两。铁丸一个。皆不得为用。封闭于库中。而没数与敌。非徒无益。反有害焉。使敌兵。围城安坐而食。被甲放丸。使我不能支吾。此古人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真我国之谓也。此无他。未尝先定所守之处。而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处。及其见失。犹不知其可惜。吁亦异矣。若使之皆储于有用之处。则粮饷不必加聚。器械不必更造。守国御敌。自有馀裕而无所忧矣。都城则既不可守矣。即今所恃者。惟是江都,南汉也。形势则非不险固。国家物力残薄。守御之具。不能处处皆备。而去京城稍远。临急之际。得达未可必。丙子南大门之危。可以鉴矣。具一或挠足。则诸司所失之物。如上所陈。然则或有事变。将无所适从。而惟当坐而待亡。终无可为之事耶。窃尝思之。不必江都,南汉。都城咫尺之地。自有形胜可守之处。而忽于至近。人自不察耳。木觅南麓。汉江北偏。自济川亭向读书堂。抱其高峰。以北至于蚕头。又转而南。从向冰库山脊。而抱其高处。以至于津边。环而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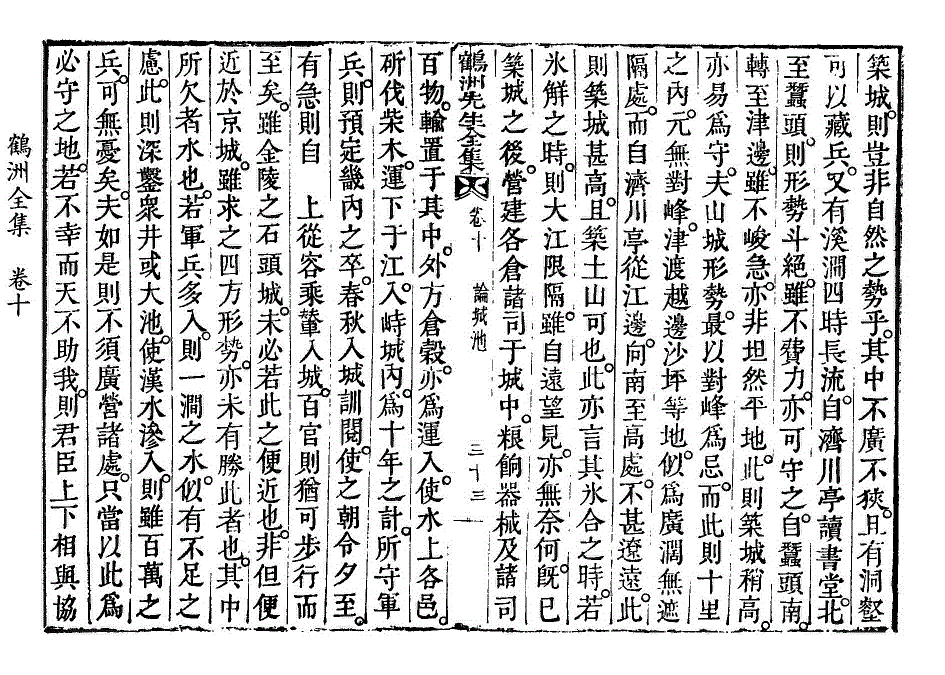 筑城。则岂非自然之势乎。其中不广不狭。且有洞壑可以藏兵。又有溪涧四时长流。自济川亭读书堂。北至蚕头。则形势斗绝。虽不费力。亦可守之。自蚕头南。转至津边。虽不峻急。亦非坦然平地。此则筑城稍高。亦易为守。夫山城形势。最以对峰为忌。而此则十里之内。元无对峰。津渡越边沙坪等地。似为广阔无遮隔处。而自济川亭从江边。向南至高处。不甚辽远。此则筑城甚高。且筑土山可也。此亦言其冰合之时。若冰解之时。则大江限隔。虽自远望见。亦无奈何。既已筑城之后。营建各仓诸司于城中。粮饷器械及诸司百物。输置于其中。外方仓谷。亦为运入。使水上各邑。斫伐柴木。运下于江。入峙城内。为十年之计。所守军兵。则预定畿内之卒。春秋入城训阅。使之朝令夕至。有急则自 上从容乘辇入城。百官则犹可步行而至矣。虽金陵之石头城。未必若此之便近也。非但便近于京城。虽求之四方形势。亦未有胜此者也。其中所欠者水也。若军兵多入。则一涧之水。似有不足之虑。此则深凿众井或大池。使汉水渗入。则虽百万之兵。可无忧矣。夫如是则不须广营诸处。只当以此为必守之地。若不幸而天不助我。则君臣上下相与协
筑城。则岂非自然之势乎。其中不广不狭。且有洞壑可以藏兵。又有溪涧四时长流。自济川亭读书堂。北至蚕头。则形势斗绝。虽不费力。亦可守之。自蚕头南。转至津边。虽不峻急。亦非坦然平地。此则筑城稍高。亦易为守。夫山城形势。最以对峰为忌。而此则十里之内。元无对峰。津渡越边沙坪等地。似为广阔无遮隔处。而自济川亭从江边。向南至高处。不甚辽远。此则筑城甚高。且筑土山可也。此亦言其冰合之时。若冰解之时。则大江限隔。虽自远望见。亦无奈何。既已筑城之后。营建各仓诸司于城中。粮饷器械及诸司百物。输置于其中。外方仓谷。亦为运入。使水上各邑。斫伐柴木。运下于江。入峙城内。为十年之计。所守军兵。则预定畿内之卒。春秋入城训阅。使之朝令夕至。有急则自 上从容乘辇入城。百官则犹可步行而至矣。虽金陵之石头城。未必若此之便近也。非但便近于京城。虽求之四方形势。亦未有胜此者也。其中所欠者水也。若军兵多入。则一涧之水。似有不足之虑。此则深凿众井或大池。使汉水渗入。则虽百万之兵。可无忧矣。夫如是则不须广营诸处。只当以此为必守之地。若不幸而天不助我。则君臣上下相与协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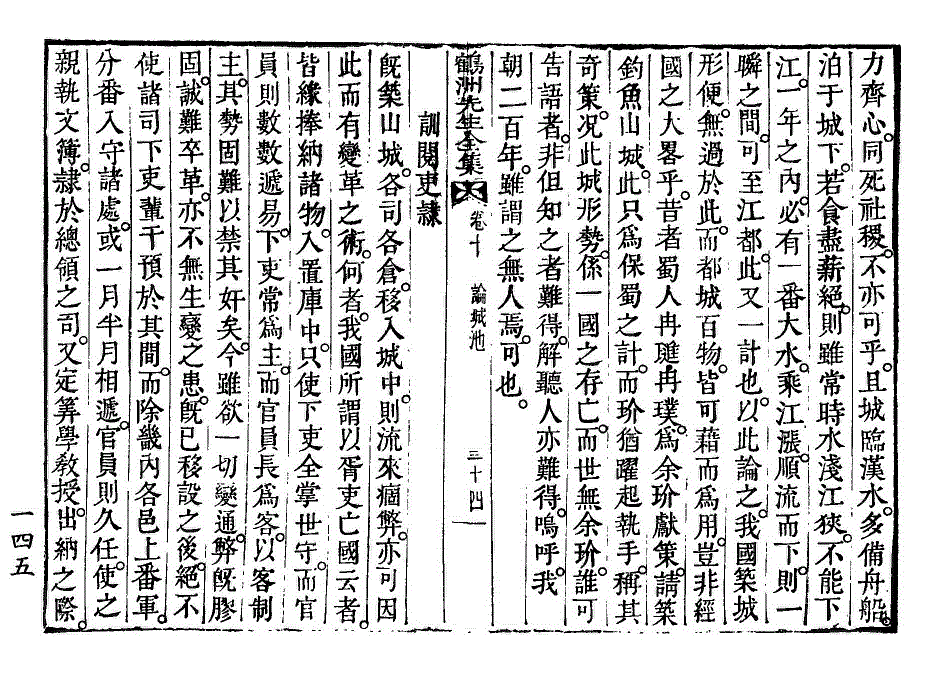 力齐心。同死社稷。不亦可乎。且城临汉水。多备舟船。泊于城下。若食尽薪绝。则虽常时水浅江狭。不能下江。一年之内。必有一番大水。乘江涨。顺流而下。则一瞬之间。可至江都。此又一计也。以此论之。我国筑城形便。无过于此。而都城百物。皆可藉而为用。岂非经国之大略乎。昔者蜀人冉琎,冉璞。为余玠献策。请筑钓鱼山城。此只为保蜀之计。而玠犹跃起执手。称其奇策。况此城形势。系一国之存亡。而世无余玠。谁可告语者。非但知之者难得。解听人亦难得。呜呼。我 朝二百年。虽谓之无人焉。可也。
力齐心。同死社稷。不亦可乎。且城临汉水。多备舟船。泊于城下。若食尽薪绝。则虽常时水浅江狭。不能下江。一年之内。必有一番大水。乘江涨。顺流而下。则一瞬之间。可至江都。此又一计也。以此论之。我国筑城形便。无过于此。而都城百物。皆可藉而为用。岂非经国之大略乎。昔者蜀人冉琎,冉璞。为余玠献策。请筑钓鱼山城。此只为保蜀之计。而玠犹跃起执手。称其奇策。况此城形势。系一国之存亡。而世无余玠。谁可告语者。非但知之者难得。解听人亦难得。呜呼。我 朝二百年。虽谓之无人焉。可也。训阅吏隶
既筑山城。各司各仓。移入城中。则流来痼弊。亦可因此而有变革之术。何者。我国所谓以胥吏亡国云者。皆缘捧纳诸物。入置库中。只使下吏全掌世守。而官员则数数递易。下吏常为主。而官员长为客。以客制主。其势固难以禁其奸矣。今虽欲一切变通。弊既胶固。诚难卒革。亦不无生变之患。既已移设之后。绝不使诸司下吏辈干预于其间。而除畿内各邑上番军。分番入守诸处。或一月半月相递。官员则久任。使之亲执文簿。隶于总领之司。又定算学教授。出纳之际。
鹤洲先生全集卷之十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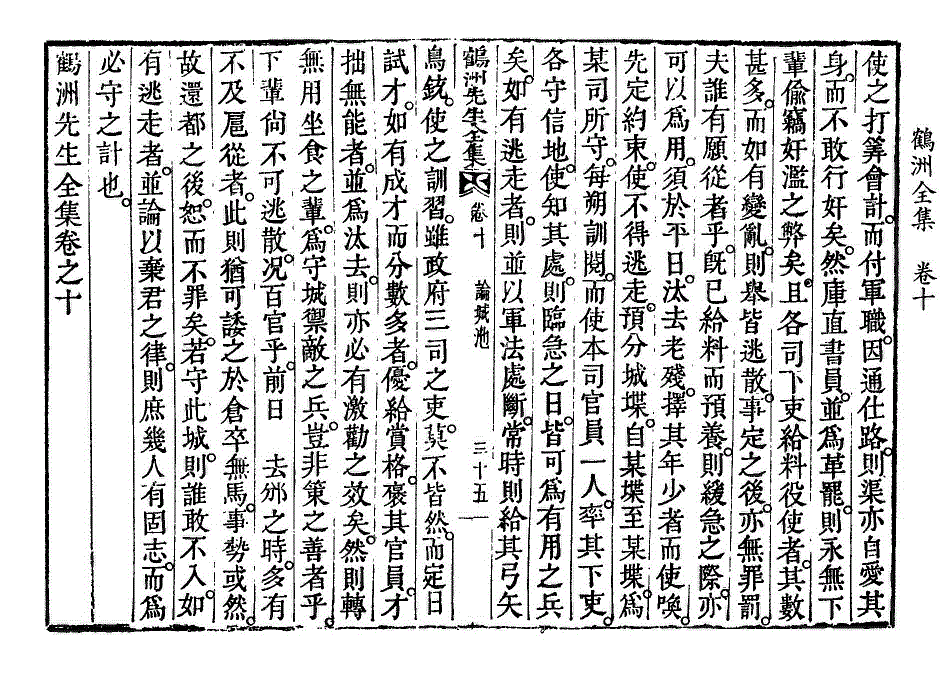 使之打算会计。而付军职。因通仕路。则渠亦自爱其身。而不敢行奸矣。然库直书员。并为革罢。则永无下辈偷窃奸滥之弊矣。且各司下吏给料役使者。其数甚多。而如有变乱。则举皆逃散。事定之后。亦无罪罚。夫谁有愿从者乎。既已给料而预养。则缓急之际。亦可以为用。须于平日。汰去老残。择其年少者而使唤。先定约束。使不得逃走。预分城堞。自某堞至某堞。为某司所守。每朔训阅。而使本司官员一人。率其下吏。各守信地。使知其处。则临急之日。皆可为有用之兵矣。如有逃走者。则并以军法处断。常时则给其弓矢鸟铳。使之训习。虽政府三司之吏。莫不皆然。而定日试才。如有成才而分数多者。优给赏格。褒其官员。才拙无能者。并为汰去。则亦必有激劝之效矣。然则转无用坐食之辈。为守城御敌之兵。岂非策之善者乎。下辈尚不可逃散。况百官乎。前日 去邠之时。多有不及扈从者。此则犹可诿之于仓卒无马。事势或然。故还都之后。恕而不罪矣。若守此城。则谁敢不入。如有逃走者。并论以弃君之律。则庶几人有固志。而为必守之计也。
使之打算会计。而付军职。因通仕路。则渠亦自爱其身。而不敢行奸矣。然库直书员。并为革罢。则永无下辈偷窃奸滥之弊矣。且各司下吏给料役使者。其数甚多。而如有变乱。则举皆逃散。事定之后。亦无罪罚。夫谁有愿从者乎。既已给料而预养。则缓急之际。亦可以为用。须于平日。汰去老残。择其年少者而使唤。先定约束。使不得逃走。预分城堞。自某堞至某堞。为某司所守。每朔训阅。而使本司官员一人。率其下吏。各守信地。使知其处。则临急之日。皆可为有用之兵矣。如有逃走者。则并以军法处断。常时则给其弓矢鸟铳。使之训习。虽政府三司之吏。莫不皆然。而定日试才。如有成才而分数多者。优给赏格。褒其官员。才拙无能者。并为汰去。则亦必有激劝之效矣。然则转无用坐食之辈。为守城御敌之兵。岂非策之善者乎。下辈尚不可逃散。况百官乎。前日 去邠之时。多有不及扈从者。此则犹可诿之于仓卒无马。事势或然。故还都之后。恕而不罪矣。若守此城。则谁敢不入。如有逃走者。并论以弃君之律。则庶几人有固志。而为必守之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