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x 页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启辞
启辞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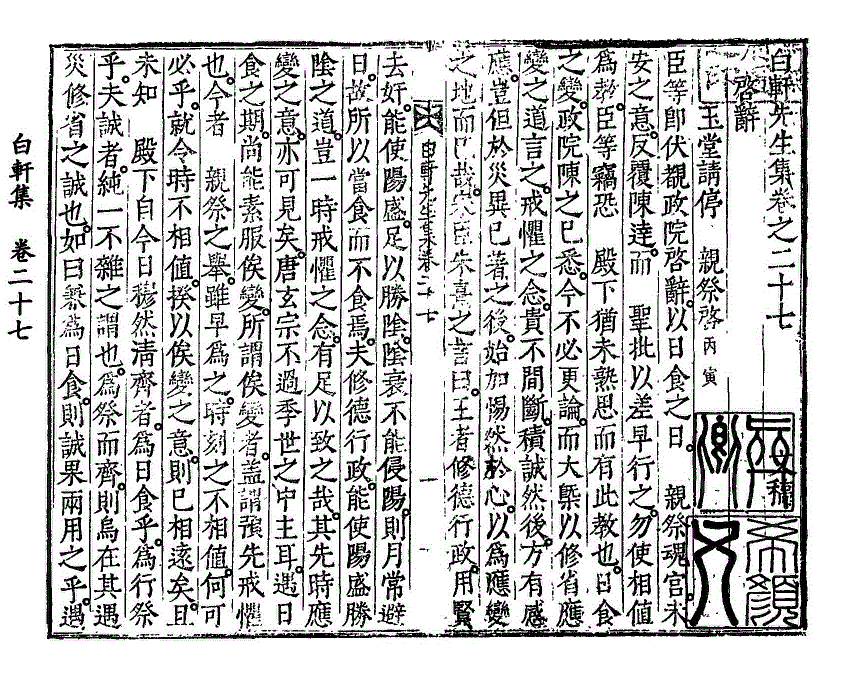 玉堂请停 亲祭启(丙寅)
玉堂请停 亲祭启(丙寅)臣等即伏睹政院启辞。以日食之日。 亲祭魂宫。未安之意。反覆陈达。而 圣批以差早行之。勿使相值为教。臣等窃恐 殿下犹未熟思而有此教也。日食之变。政院陈之已悉。今不必更论。而大槩以修省应变之道言之。戒惧之念。贵不间断。积诚然后。方有感应。岂但于灾异已著之后。始加惕然于心。以为应变之地而已哉。宋臣朱熹之言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月常避日。故所以当食而不食焉。夫修德行政。能使阳盛胜阴之道。岂一时戒惧之念。有足以致之哉。其先时应变之意。亦可见矣。唐玄宗不过季世之中主耳。遇日食之期。尚能素服俟变。所谓俟变者。盖谓预先戒惧也。今者 亲祭之举。虽早为之。时刻之不相值。何可必乎。就令时不相值。揆以俟变之意。则已相远矣。且未知 殿下自今日穆然清齐者。为日食乎。为行祭乎。夫诚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为祭而齐。则乌在其遇灾修省之诚也。如曰兼为日食。则诚果两用之乎。遇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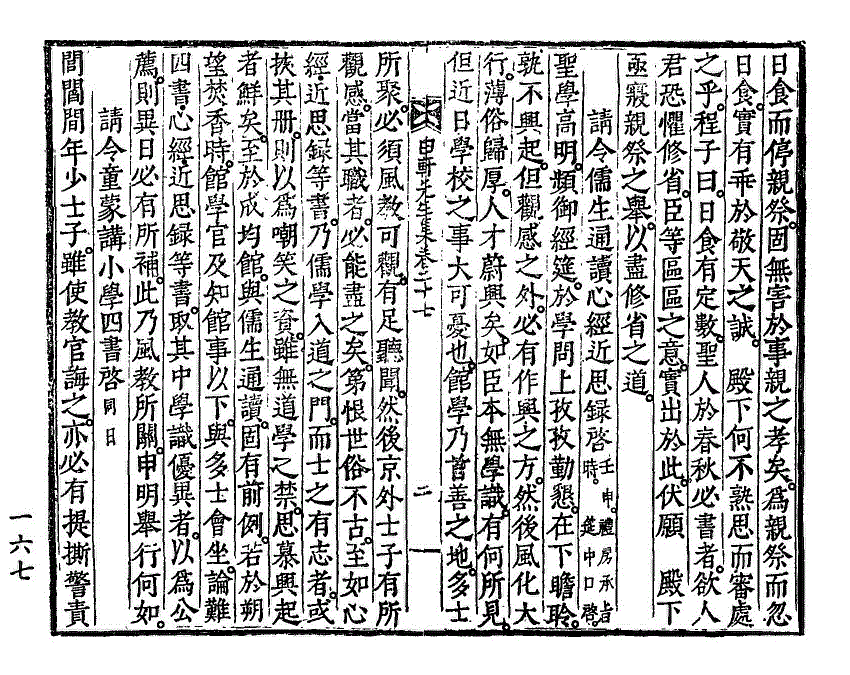 日食而停亲祭。固无害于事亲之孝矣。为亲祭而忽日食。实有乖于敬天之诚。 殿下何不熟思而审处之乎。程子曰。日食有定数。圣人于春秋必书者。欲人君恐惧修省。臣等区区之意。实出于此。伏愿 殿下亟寝亲祭之举。以尽修省之道。
日食而停亲祭。固无害于事亲之孝矣。为亲祭而忽日食。实有乖于敬天之诚。 殿下何不熟思而审处之乎。程子曰。日食有定数。圣人于春秋必书者。欲人君恐惧修省。臣等区区之意。实出于此。伏愿 殿下亟寝亲祭之举。以尽修省之道。请令儒生通读心经近思录启(壬申。礼房承旨时。 筵中口启。)
圣学高明。频御经筵。于学问上孜孜勤恳。在下瞻聆。孰不兴起。但观感之外。必有作兴之方。然后风化大行。薄俗归厚。人才蔚兴矣。如臣本无学识。有何所见。但近日学校之事大可忧也。馆学乃首善之地。多士所聚。必须风教可观。有足听闻。然后京外士子有所观感。当其职者。必能尽之矣。第恨世俗不古。至如心经,近思录等书。乃儒学入道之门。而士之有志者。或豗其册。则以为嘲笑之资。虽无道学之禁。思慕兴起者鲜矣。至于成均馆。与儒生通读。固有前例。若于朔望焚香时。馆学官及知馆事以下。与多士会坐。论难四书,心经,近思录等书。取其中学识优异者。以为公荐。则异日必有所补。此乃风教所关。申明举行何如。
请令童蒙讲小学四书启(壬申)
闾阎间年少士子。虽使教官诲之。亦必有提撕警责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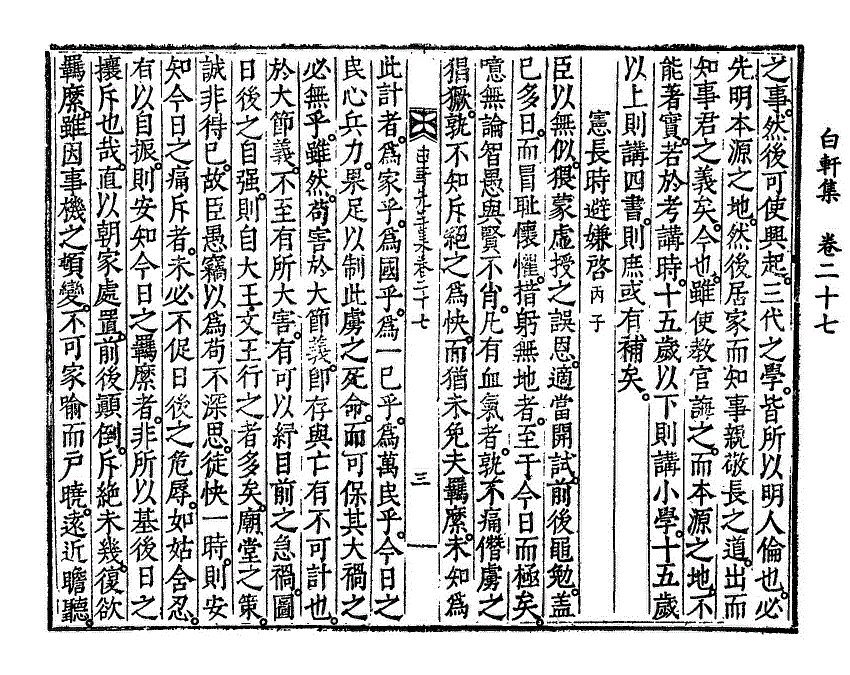 之事。然后可使兴起。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必先明本源之地。然后居家而知事亲敬长之道。出而知事君之义矣。今也。虽使教官诲之。而本源之地。不能著实。若于考讲时。十五岁以下则讲小学。十五岁以上则讲四书。则庶或有补矣。
之事。然后可使兴起。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必先明本源之地。然后居家而知事亲敬长之道。出而知事君之义矣。今也。虽使教官诲之。而本源之地。不能著实。若于考讲时。十五岁以下则讲小学。十五岁以上则讲四书。则庶或有补矣。宪长时避嫌启(丙子)
臣以无似。猥蒙虚授之误恩。适当开试。前后黾勉。盖已多日。而冒耻怀惧。措躬无地者。至于今日而极矣。噫无论智愚与贤不肖。凡有血气者。孰不痛僭虏之猖獗。孰不知斥绝之为快。而犹未免夫羁縻。未知为此计者。为家乎。为国乎。为一己乎。为万民乎。今日之民心兵力。果足以制此虏之死命。而可保其大祸之必无乎。虽然。苟害于大节义。即存与亡有不可计也。于大节义。不至有所大害。有可以纾目前之急祸。图日后之自强。则自大王,文王行之者多矣。庙堂之策。诚非得已。故臣愚窃以为苟不深思。徒快一时。则安知今日之痛斥者。未必不促日后之危辱。如姑含忍。有以自振。则安知今日之羁縻者。非所以基后日之攘斥也哉。直以朝家处置。前后颠倒。斥绝未几。复欲羁縻。虽因事机之顿变。不可家喻而户晓。远近瞻听。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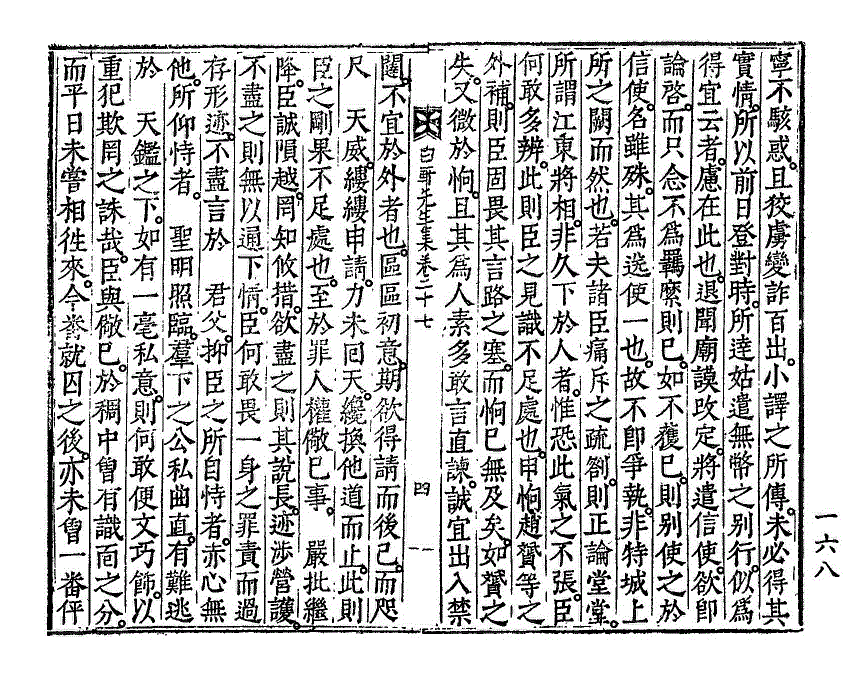 宁不骇惑。且狡虏变诈百出。小译之所传。未必得其实情。所以前日登对时。所达姑遣无币之别行。似为得宜云者。虑在此也。退闻庙谟改定。将遣信使。欲即论启。而只念不为羁縻则已。如不获已。则别使之于信使。名虽殊。其为送使一也。故不即争执。非特城上所之阙而然也。若夫诸臣痛斥之疏劄。则正论堂堂。所谓江东将相。非久下于人者。惟恐此气之不张。臣何敢多辨。此则臣之见识不足处也。申恦,赵赟等之外补。则臣固畏其言路之塞。而恦已无及矣。如赟之失。又微于恦。且其为人素多敢言直谏。诚宜出入禁闼。不宜于外者也。区区初意。期欲得请而后已。而咫尺 天威。缕缕申请。力未回天。才换他道而止。此则臣之刚果不足处也。至于罪人权儆己事。 严批继降。臣诚陨越。罔知攸措。欲尽之则其说长。迹涉营护。不尽之则无以通下情。臣何敢畏一身之罪责而过存形迹。不尽言于 君父。抑臣之所自恃者。赤心无他。所仰恃者。 圣明照临。群下之公私曲直。有难逃于 天鉴之下。如有一毫私意。则何敢便文巧饰。以重犯欺罔之诛哉。臣与儆己。于稠中曾有识面之分。而平日未尝相往来。今番就囚之后。亦未曾一番伻
宁不骇惑。且狡虏变诈百出。小译之所传。未必得其实情。所以前日登对时。所达姑遣无币之别行。似为得宜云者。虑在此也。退闻庙谟改定。将遣信使。欲即论启。而只念不为羁縻则已。如不获已。则别使之于信使。名虽殊。其为送使一也。故不即争执。非特城上所之阙而然也。若夫诸臣痛斥之疏劄。则正论堂堂。所谓江东将相。非久下于人者。惟恐此气之不张。臣何敢多辨。此则臣之见识不足处也。申恦,赵赟等之外补。则臣固畏其言路之塞。而恦已无及矣。如赟之失。又微于恦。且其为人素多敢言直谏。诚宜出入禁闼。不宜于外者也。区区初意。期欲得请而后已。而咫尺 天威。缕缕申请。力未回天。才换他道而止。此则臣之刚果不足处也。至于罪人权儆己事。 严批继降。臣诚陨越。罔知攸措。欲尽之则其说长。迹涉营护。不尽之则无以通下情。臣何敢畏一身之罪责而过存形迹。不尽言于 君父。抑臣之所自恃者。赤心无他。所仰恃者。 圣明照临。群下之公私曲直。有难逃于 天鉴之下。如有一毫私意。则何敢便文巧饰。以重犯欺罔之诛哉。臣与儆己。于稠中曾有识面之分。而平日未尝相往来。今番就囚之后。亦未曾一番伻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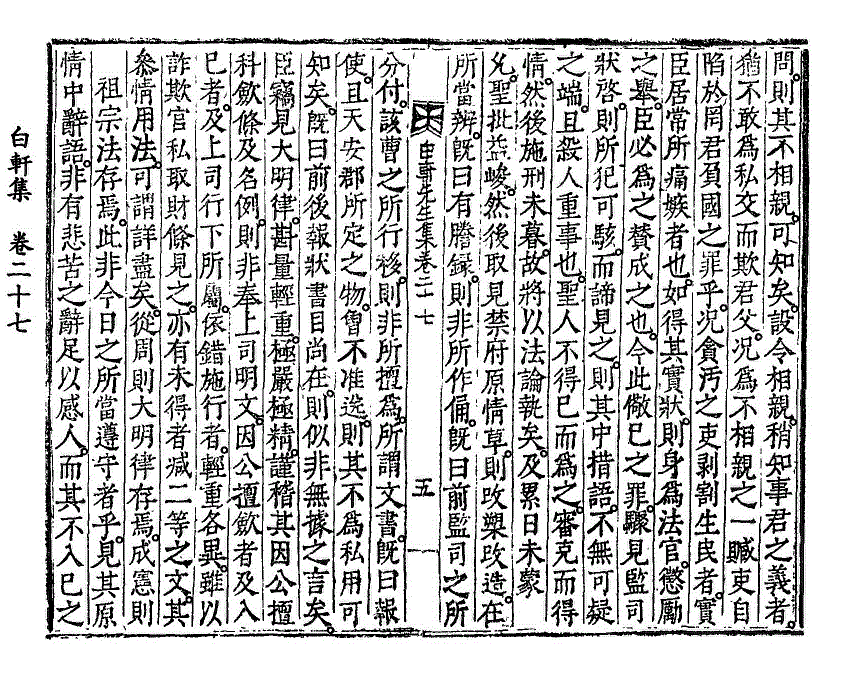 问。则其不相亲。可知矣。设令相亲。稍知事君之义者。犹不敢为私交而欺君父。况为不相亲之一赃吏自陷于罔君负国之罪乎。况贪污之吏剥割生民者。实臣居常所痛嫉者也。如得其实状。则身为法官。惩励之举。臣必为之赞成之也。今此儆己之罪。骤见监司状启。则所犯可骇。而谛见之。则其中措语。不无可疑之端。且杀人重事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审克而得情。然后施刑未暮。故将以法论执矣。及累日未蒙 允。圣批益峻。然后取见禁府原情草。则改槊改造。在所当辨。既曰有誊录。则非所作俑。既曰前监司之所分付。该曹之所行移。则非所擅为。所谓文书。既曰报使。且天安郡所定之物。曾不准送。则其不为私用可知矣。既曰前后报状书目尚在。则似非无据之言矣。臣窃见大明律。斟量轻重。极严极精。谨稽其因公擅科敛条及名例。则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敛者及入己者。及上司行下所属。依错施行者。轻重各异。虽以诈欺官私取财条见之。亦有未得者减二等之文。其参情用法。可谓详尽矣。从周则大明律存焉。成宪则 祖宗法存焉。此非今日之所当遵守者乎。见其原情中辞语。非有悲苦之辞足以感人。而其不入己之
问。则其不相亲。可知矣。设令相亲。稍知事君之义者。犹不敢为私交而欺君父。况为不相亲之一赃吏自陷于罔君负国之罪乎。况贪污之吏剥割生民者。实臣居常所痛嫉者也。如得其实状。则身为法官。惩励之举。臣必为之赞成之也。今此儆己之罪。骤见监司状启。则所犯可骇。而谛见之。则其中措语。不无可疑之端。且杀人重事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审克而得情。然后施刑未暮。故将以法论执矣。及累日未蒙 允。圣批益峻。然后取见禁府原情草。则改槊改造。在所当辨。既曰有誊录。则非所作俑。既曰前监司之所分付。该曹之所行移。则非所擅为。所谓文书。既曰报使。且天安郡所定之物。曾不准送。则其不为私用可知矣。既曰前后报状书目尚在。则似非无据之言矣。臣窃见大明律。斟量轻重。极严极精。谨稽其因公擅科敛条及名例。则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敛者及入己者。及上司行下所属。依错施行者。轻重各异。虽以诈欺官私取财条见之。亦有未得者减二等之文。其参情用法。可谓详尽矣。从周则大明律存焉。成宪则 祖宗法存焉。此非今日之所当遵守者乎。见其原情中辞语。非有悲苦之辞足以感人。而其不入己之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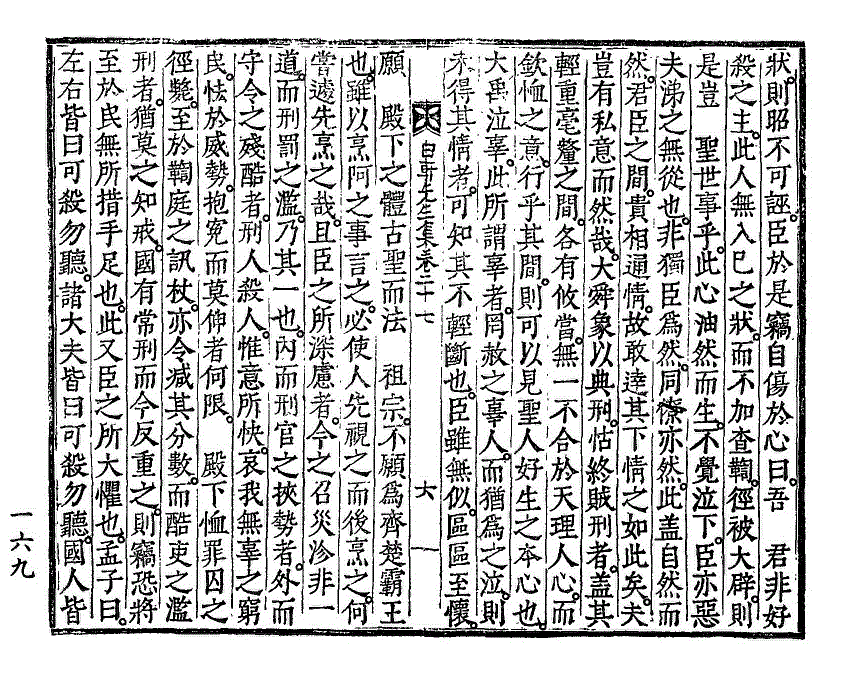 状。则昭不可诬。臣于是窃自伤于心曰。吾 君非好杀之主。此人无入己之状。而不加查鞫。径被大辟。则是岂 圣世事乎。此心油然而生。不觉泣下。臣亦恶夫涕之无从也。非独臣为然。同僚亦然。此盖自然而然。君臣之间。贵相通情。故敢达其下情之如此矣。夫岂有私意而然哉。大舜象以典刑。怙终贼刑者。盖其轻重毫釐之间。各有攸当。无一不合于天理人心。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也。大禹泣辜。此所谓辜者。罔赦之辜人。而犹为之泣。则未得其情者。可知其不轻断也。臣虽无似。区区至怀。愿 殿下之体古圣而法 祖宗。不愿为齐楚霸王也。虽以烹阿之事言之。必使人先视之而后烹之。何尝遽先烹之哉。且臣之所深虑者。今之召灾沴非一道。而刑罚之滥。乃其一也。内而刑官之挟势者。外而守令之残酷者。刑人杀人。惟意所快。哀我无辜之穷民。怯于威势。抱冤而莫伸者何限。 殿下恤罪囚之径毙。至于鞫庭之讯杖。亦令减其分数。而酷吏之滥刑者。犹莫之知戒。国有常刑而今反重之。则窃恐将至于民无所措手足也。此又臣之所大惧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
状。则昭不可诬。臣于是窃自伤于心曰。吾 君非好杀之主。此人无入己之状。而不加查鞫。径被大辟。则是岂 圣世事乎。此心油然而生。不觉泣下。臣亦恶夫涕之无从也。非独臣为然。同僚亦然。此盖自然而然。君臣之间。贵相通情。故敢达其下情之如此矣。夫岂有私意而然哉。大舜象以典刑。怙终贼刑者。盖其轻重毫釐之间。各有攸当。无一不合于天理人心。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也。大禹泣辜。此所谓辜者。罔赦之辜人。而犹为之泣。则未得其情者。可知其不轻断也。臣虽无似。区区至怀。愿 殿下之体古圣而法 祖宗。不愿为齐楚霸王也。虽以烹阿之事言之。必使人先视之而后烹之。何尝遽先烹之哉。且臣之所深虑者。今之召灾沴非一道。而刑罚之滥。乃其一也。内而刑官之挟势者。外而守令之残酷者。刑人杀人。惟意所快。哀我无辜之穷民。怯于威势。抱冤而莫伸者何限。 殿下恤罪囚之径毙。至于鞫庭之讯杖。亦令减其分数。而酷吏之滥刑者。犹莫之知戒。国有常刑而今反重之。则窃恐将至于民无所措手足也。此又臣之所大惧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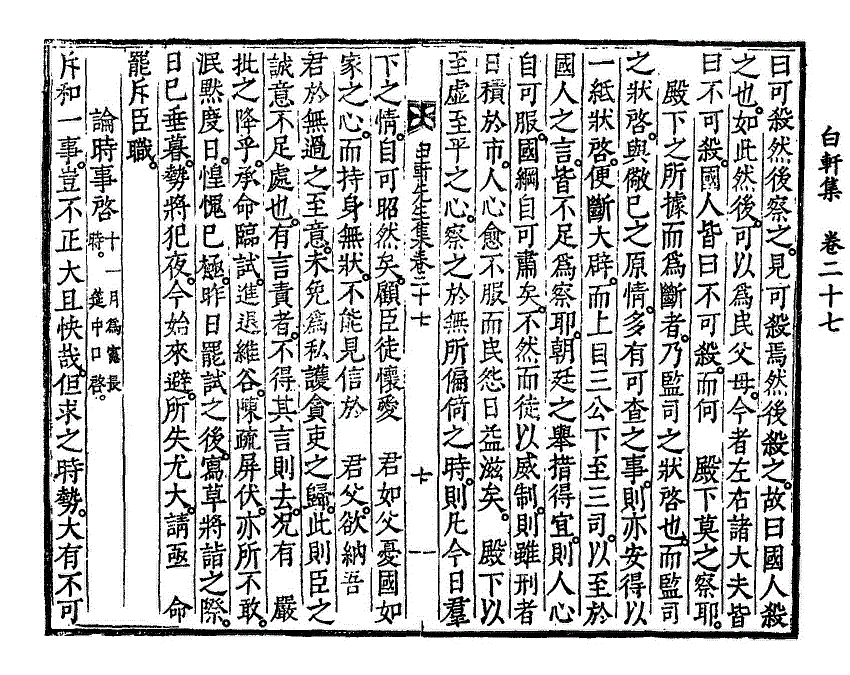 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今者左右诸大夫皆曰不可杀。国人皆曰不可杀。而何 殿下莫之察耶。 殿下之所据而为断者。乃监司之状启也。而监司之状启。与儆己之原情。多有可查之事。则亦安得以一纸状启。便断大辟。而上目三公下至三司。以至于国人之言。皆不足为察耶。朝廷之举措得宜。则人心自可服。国纲自可肃矣。不然而徒以威制。则虽刑者日积于市。人心愈不服而民怨日益滋矣。 殿下以至虚至平之心。察之于无所偏倚之时。则凡今日群下之情。自可昭然矣。顾臣徒怀爱 君如父忧国如家之心。而持身无状。不能见信于 君父。欲纳吾 君于无过之至意。未免为私护贪吏之归。此则臣之诚意不足处也。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况有 严批之降乎。承命临试。进退维谷。陈疏屏伏。亦所不敢。泯默度日。惶愧已极。昨日罢试之后。写草将诣之际。日已垂暮。势将犯夜。今始来避。所失尤大。请亟 命罢斥臣职。
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今者左右诸大夫皆曰不可杀。国人皆曰不可杀。而何 殿下莫之察耶。 殿下之所据而为断者。乃监司之状启也。而监司之状启。与儆己之原情。多有可查之事。则亦安得以一纸状启。便断大辟。而上目三公下至三司。以至于国人之言。皆不足为察耶。朝廷之举措得宜。则人心自可服。国纲自可肃矣。不然而徒以威制。则虽刑者日积于市。人心愈不服而民怨日益滋矣。 殿下以至虚至平之心。察之于无所偏倚之时。则凡今日群下之情。自可昭然矣。顾臣徒怀爱 君如父忧国如家之心。而持身无状。不能见信于 君父。欲纳吾 君于无过之至意。未免为私护贪吏之归。此则臣之诚意不足处也。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况有 严批之降乎。承命临试。进退维谷。陈疏屏伏。亦所不敢。泯默度日。惶愧已极。昨日罢试之后。写草将诣之际。日已垂暮。势将犯夜。今始来避。所失尤大。请亟 命罢斥臣职。论时事启(十一月为宪长时。 筵中口启。)
斥和一事。岂不正大且快哉。但求之时势。大有不可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0L 页
 者。当今国家之事。无一事可恃。而至于民生离怨。则尤不忍言矣。虽不知人人皆然。而两西之人。至曰贼何不来。贼来吾活。此言岂不痛心乎。虽至愚之人。岂不知贼来之不利乎。然犹为此言者。赋役重而人不聊生故也。至于畿甸三南。无处不然云。自 上尽蠲御供。图治如渴。而民心离散。至于如此。当此之时。不顾兵力之单。民心之散。不计时势之缓急本末。只以堂堂大义言之。此言大义所在也。固为好矣。如彼狂贼。岂观他国之弊乎。书生之见。虽甚迂缓。凡事不出于事理之外。不顾时势。横挑强寇。其来也必以冬冰渡鸭江。利在速进。不数日。直薄京都。则所恃者惟有江都。而三军百僚尽渡然后可以守之。一日一渡之江。其能尽渡乎。冰江阻前。而飘风骤雨之势隳突于后。则祸迫之后。置君父于何地乎。三韩一草一木。皆 皇朝之赐也。大义所在。人谁不知。而事有缓急本末。何可不思乎。汉唐方盛之时。堂堂国势。兵力何所可畏。名臣猛将。相望于朝。而犹有和戎之举。况于今日乎。当初龙胡之走也。我国如送一使。以为丁卯约誓之时。至于告天为之。而尔国何自遽为称帝。欲绝和好乎。汝国既已绝和。我国亦当绝之。而我国则告
者。当今国家之事。无一事可恃。而至于民生离怨。则尤不忍言矣。虽不知人人皆然。而两西之人。至曰贼何不来。贼来吾活。此言岂不痛心乎。虽至愚之人。岂不知贼来之不利乎。然犹为此言者。赋役重而人不聊生故也。至于畿甸三南。无处不然云。自 上尽蠲御供。图治如渴。而民心离散。至于如此。当此之时。不顾兵力之单。民心之散。不计时势之缓急本末。只以堂堂大义言之。此言大义所在也。固为好矣。如彼狂贼。岂观他国之弊乎。书生之见。虽甚迂缓。凡事不出于事理之外。不顾时势。横挑强寇。其来也必以冬冰渡鸭江。利在速进。不数日。直薄京都。则所恃者惟有江都。而三军百僚尽渡然后可以守之。一日一渡之江。其能尽渡乎。冰江阻前。而飘风骤雨之势隳突于后。则祸迫之后。置君父于何地乎。三韩一草一木。皆 皇朝之赐也。大义所在。人谁不知。而事有缓急本末。何可不思乎。汉唐方盛之时。堂堂国势。兵力何所可畏。名臣猛将。相望于朝。而犹有和戎之举。况于今日乎。当初龙胡之走也。我国如送一使。以为丁卯约誓之时。至于告天为之。而尔国何自遽为称帝。欲绝和好乎。汝国既已绝和。我国亦当绝之。而我国则告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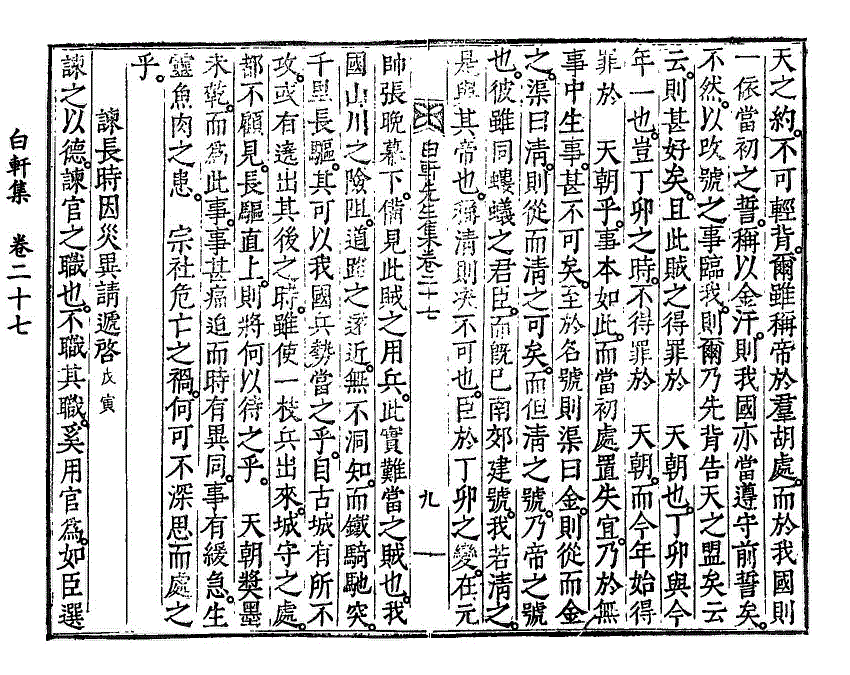 天之约。不可轻背。尔虽称帝于群胡处。而于我国则一依当初之誓。称以金汗。则我国亦当遵守前誓矣。不然。以改号之事临我。则尔乃先背告天之盟矣云云。则甚好矣。且此贼之得罪于 天朝也。丁卯与今年一也。岂丁卯之时。不得罪于 天朝。而今年始得罪于 天朝乎。事本如此。而当初处置失宜。乃于无事中生事。甚不可矣。至于名号则渠曰金。则从而金之。渠曰清。则从而清之可矣。而但清之号。乃帝之号也。彼虽同蝼蚁之君臣。而既已南郊建号。我若清之。是与其帝也。称清则决不可也。臣于丁卯之变。在元帅张晚幕下。备见此贼之用兵。此实难当之贼也。我国山川之险阻。道路之远近。无不洞知。而铁骑驰突。千里长驱。其可以我国兵势当之乎。自古城有所不攻。或有绕出其后之时。虽使一枝兵出来。城守之处。都不顾见。长驱直上。则将何以待之乎。 天朝奖墨未乾。而为此事。事甚痛迫而时有异同。事有缓急。生灵鱼肉之患。 宗社危亡之祸。何可不深思而处之乎。
天之约。不可轻背。尔虽称帝于群胡处。而于我国则一依当初之誓。称以金汗。则我国亦当遵守前誓矣。不然。以改号之事临我。则尔乃先背告天之盟矣云云。则甚好矣。且此贼之得罪于 天朝也。丁卯与今年一也。岂丁卯之时。不得罪于 天朝。而今年始得罪于 天朝乎。事本如此。而当初处置失宜。乃于无事中生事。甚不可矣。至于名号则渠曰金。则从而金之。渠曰清。则从而清之可矣。而但清之号。乃帝之号也。彼虽同蝼蚁之君臣。而既已南郊建号。我若清之。是与其帝也。称清则决不可也。臣于丁卯之变。在元帅张晚幕下。备见此贼之用兵。此实难当之贼也。我国山川之险阻。道路之远近。无不洞知。而铁骑驰突。千里长驱。其可以我国兵势当之乎。自古城有所不攻。或有绕出其后之时。虽使一枝兵出来。城守之处。都不顾见。长驱直上。则将何以待之乎。 天朝奖墨未乾。而为此事。事甚痛迫而时有异同。事有缓急。生灵鱼肉之患。 宗社危亡之祸。何可不深思而处之乎。谏长时因灾异请递启(戊寅)
谏之以德。谏官之职也。不职其职。奚用官为。如臣选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1L 页
 愞试之素矣。休论既往。即乱后忝据言地者。非止一再。而曾无尺寸效期期之言。人或咎之。如屋之嗔。丛萃于身。虽 殿下之好察。亦何所取而动四聪之听哉。臣之不宜复居此地。已较著矣。况今日国事。如水火之益深热。馀烬惨目。大命且迫。愁民岁旷。愁气日滋。屋下之谈。无不寒心。而何曾有草野尺纸书。乃一投于公车者乎。呜呼。人心大可见矣。重以灾沴之作。愈往愈酷。白虹贯日。变异之尤惨者。何为而又发于冱寒之时也。然上天之慇勤乎 殿下者。亦已至矣。是宜上下惊遑。交相脩戒。汲汲然谋所以感动乎人心。悦豫乎天意。而侧耳累日。未闻有一人警欬乎 殿下之侧者。是朝廷之上。言路杜矣。应文之事。亦随而废矣。无怪乎草野之寥寥也。国家之忧于是乎弥大。愚臣之虑至此而益切。 殿下可不反躬而惕然于心乎。臣愚窃以为此非循常袭例之时。夫三光垂异。擢士为相。四夷侵陵。拔卒为将。急贤渴能。年格奚问。为今之计。莫如简一时贤良方正之士。擢置辅导言责之地。使之精心白意。尽言极谏。虚 殿下之襟而施之如不及。则其庶几。而臣而尚可叨此任于此时乎。请 命递臣职。以授其人。
愞试之素矣。休论既往。即乱后忝据言地者。非止一再。而曾无尺寸效期期之言。人或咎之。如屋之嗔。丛萃于身。虽 殿下之好察。亦何所取而动四聪之听哉。臣之不宜复居此地。已较著矣。况今日国事。如水火之益深热。馀烬惨目。大命且迫。愁民岁旷。愁气日滋。屋下之谈。无不寒心。而何曾有草野尺纸书。乃一投于公车者乎。呜呼。人心大可见矣。重以灾沴之作。愈往愈酷。白虹贯日。变异之尤惨者。何为而又发于冱寒之时也。然上天之慇勤乎 殿下者。亦已至矣。是宜上下惊遑。交相脩戒。汲汲然谋所以感动乎人心。悦豫乎天意。而侧耳累日。未闻有一人警欬乎 殿下之侧者。是朝廷之上。言路杜矣。应文之事。亦随而废矣。无怪乎草野之寥寥也。国家之忧于是乎弥大。愚臣之虑至此而益切。 殿下可不反躬而惕然于心乎。臣愚窃以为此非循常袭例之时。夫三光垂异。擢士为相。四夷侵陵。拔卒为将。急贤渴能。年格奚问。为今之计。莫如简一时贤良方正之士。擢置辅导言责之地。使之精心白意。尽言极谏。虚 殿下之襟而施之如不及。则其庶几。而臣而尚可叨此任于此时乎。请 命递臣职。以授其人。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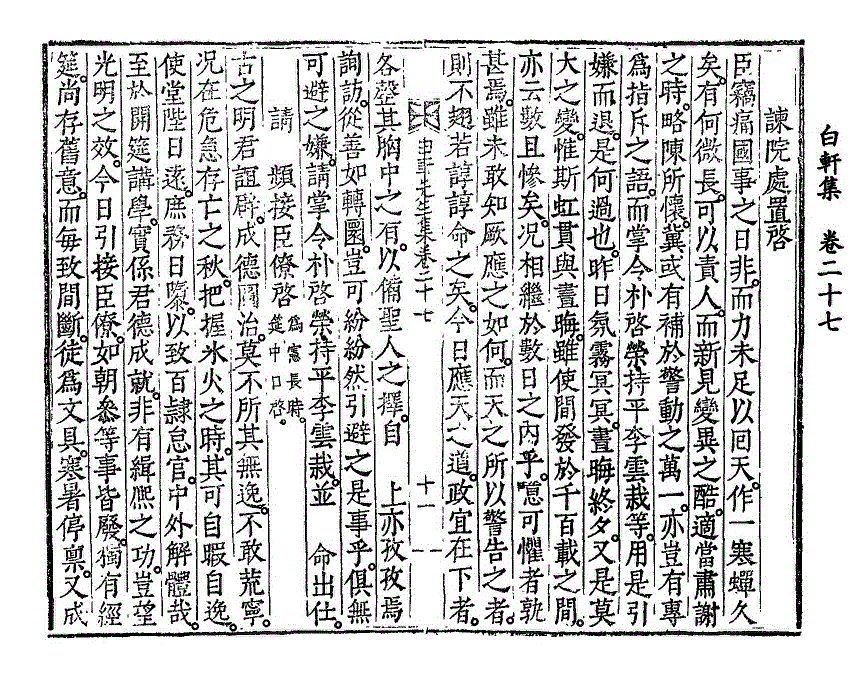 谏院处置启
谏院处置启臣窃痛国事之日非。而力未足以回天。作一寒蝉久矣。有何微长。可以责人。而新见变异之酷。适当肃谢之时。略陈所怀。冀或有补于警动之万一。亦岂有专为指斥之语。而掌令朴启荣,持平李云栽等。用是引嫌而退。是何过也。昨日氛雾冥冥。昼晦终夕。又是莫大之变。惟斯虹贯与昼晦。虽使间发于千百载之间。亦云数且惨矣。况相继于数日之内乎。噫可惧者孰甚焉。虽未敢知厥应之如何。而天之所以警告之者。则不翅若谆谆命之矣。今日应天之道。政宜在下者。各罄其胸中之有。以备圣人之择。自 上亦孜孜焉询访。从善如转圜。岂可纷纷然引避之是事乎。俱无可避之嫌。请掌令朴启荣,持平李云栽。并 命出仕。
请 频接臣僚启(为宪长时。筵中口启。)
古之明君谊辟。成德图治。莫不所其无逸。不敢荒宁。况在危急存亡之秋。把握冰火之时。其可自暇自逸。使堂陛日远。庶务日隳。以致百隶怠官。中外解体哉。至于开筵讲学。实系君德成就。非有缉熙之功。岂望光明之效。今日引接臣僚。如朝参等事皆废。独有经筵。尚存旧意。而每致间断。徒为文具。寒暑停禀。又成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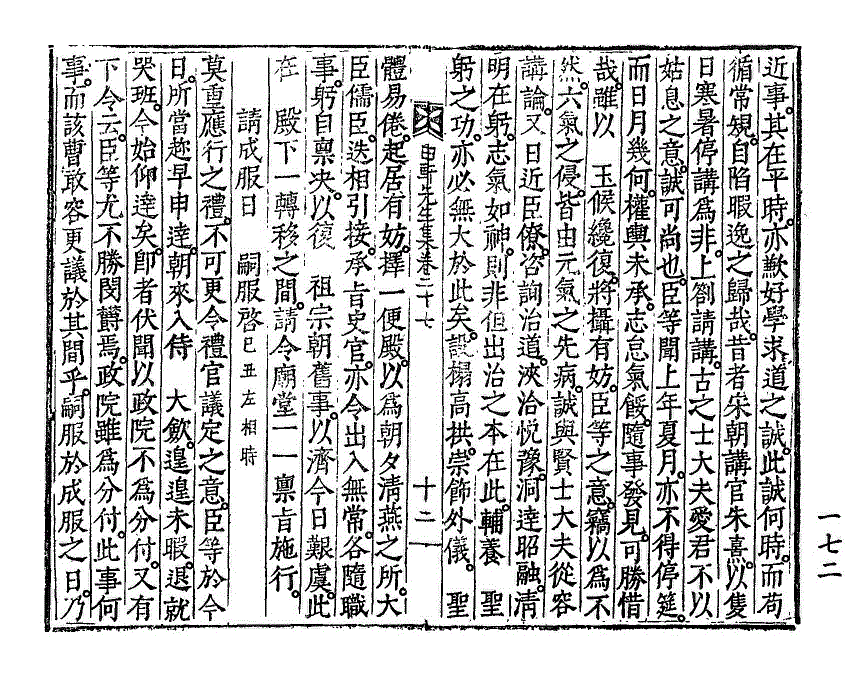 近事。其在平时。亦歉好学求道之诚。此诚何时。而苟循常规。自陷暇逸之归哉。昔者宋朝讲官朱熹。以只日寒暑停讲为非。上劄请讲。古之士大夫爱君不以姑息之意。诚可尚也。臣等闻上年夏月。亦不得停筵。而日月几何。权舆未承。志怠气馁。随事发见。可胜惜哉。虽以 玉候才复。将摄有妨。臣等之意。窃以为不然。六气之侵。皆由元气之先病。诚与贤士大夫从容讲论。又日近臣僚。咨询治道。浃洽悦豫。洞达昭融。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非但出治之本在此。辅养 圣躬之功。亦必无大于此矣。设榻高拱。崇饰外仪。 圣体易倦。起居有妨。择一便殿。以为朝夕清燕之所。大臣儒臣。迭相引接。承旨史官。亦令出入无常。各随职事。躬自禀决。以复 祖宗朝旧事。以济今日艰虞。此在 殿下一转移之间。请令庙堂一一禀旨施行。
近事。其在平时。亦歉好学求道之诚。此诚何时。而苟循常规。自陷暇逸之归哉。昔者宋朝讲官朱熹。以只日寒暑停讲为非。上劄请讲。古之士大夫爱君不以姑息之意。诚可尚也。臣等闻上年夏月。亦不得停筵。而日月几何。权舆未承。志怠气馁。随事发见。可胜惜哉。虽以 玉候才复。将摄有妨。臣等之意。窃以为不然。六气之侵。皆由元气之先病。诚与贤士大夫从容讲论。又日近臣僚。咨询治道。浃洽悦豫。洞达昭融。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非但出治之本在此。辅养 圣躬之功。亦必无大于此矣。设榻高拱。崇饰外仪。 圣体易倦。起居有妨。择一便殿。以为朝夕清燕之所。大臣儒臣。迭相引接。承旨史官。亦令出入无常。各随职事。躬自禀决。以复 祖宗朝旧事。以济今日艰虞。此在 殿下一转移之间。请令庙堂一一禀旨施行。请成服日 嗣服启(己丑左相时)
莫重应行之礼。不可更令礼官议定之意。臣等于今日。所当趁早申达。朝来入侍 大敛。遑遑未暇。退就哭班。今始仰达矣。即者伏闻以政院不为分付。又有下令云。臣等尤不胜闵郁焉。政院虽为分付。此事何事。而该曹敢容更议于其间乎。嗣服于成服之日。乃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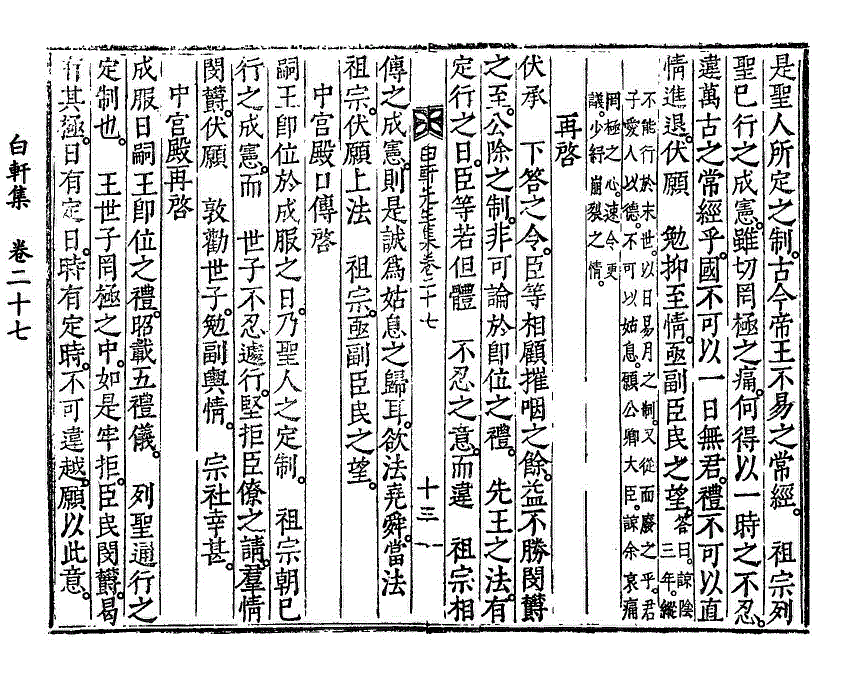 是圣人所定之制。古今帝王不易之常经。 祖宗列圣已行之成宪。虽切罔极之痛。何得以一时之不忍。违万古之常经乎。国不可以一日无君。礼不可以直情进退。伏愿 勉抑至情。亟副臣民之望。(答曰。谅阴三年。纵不能行于末世。以日易月之制。又从而废之乎。君子爱人以德。不可以姑息。愿公卿大臣。谅余哀痛罔极之心。速令更议。少纾崩裂之情。)
是圣人所定之制。古今帝王不易之常经。 祖宗列圣已行之成宪。虽切罔极之痛。何得以一时之不忍。违万古之常经乎。国不可以一日无君。礼不可以直情进退。伏愿 勉抑至情。亟副臣民之望。(答曰。谅阴三年。纵不能行于末世。以日易月之制。又从而废之乎。君子爱人以德。不可以姑息。愿公卿大臣。谅余哀痛罔极之心。速令更议。少纾崩裂之情。)请成服日 嗣服启(己丑左相时)[再启]
伏承 下答之令。臣等相顾摧咽之馀。益不胜闵郁之至。公除之制。非可论于即位之礼。 先王之法。有定行之日。臣等若但体 不忍之意。而违 祖宗相传之成宪。则是诚为姑息之归耳。欲法尧舜。当法 祖宗。伏愿上法 祖宗。亟副臣民之望。
中宫殿口传启
嗣王即位于成服之日。乃圣人之定制。 祖宗朝已行之成宪。而 世子不忍遽行。坚拒臣僚之请。群情闵郁。伏愿 敦劝世子。勉副舆情。 宗社幸甚。
中宫殿再启
成服日嗣王即位之礼。昭载五礼仪。 列圣通行之定制也。 王世子罔极之中。如是牢拒。臣民闵郁。曷有其极。日有定日。时有定时。不可违越。愿以此意。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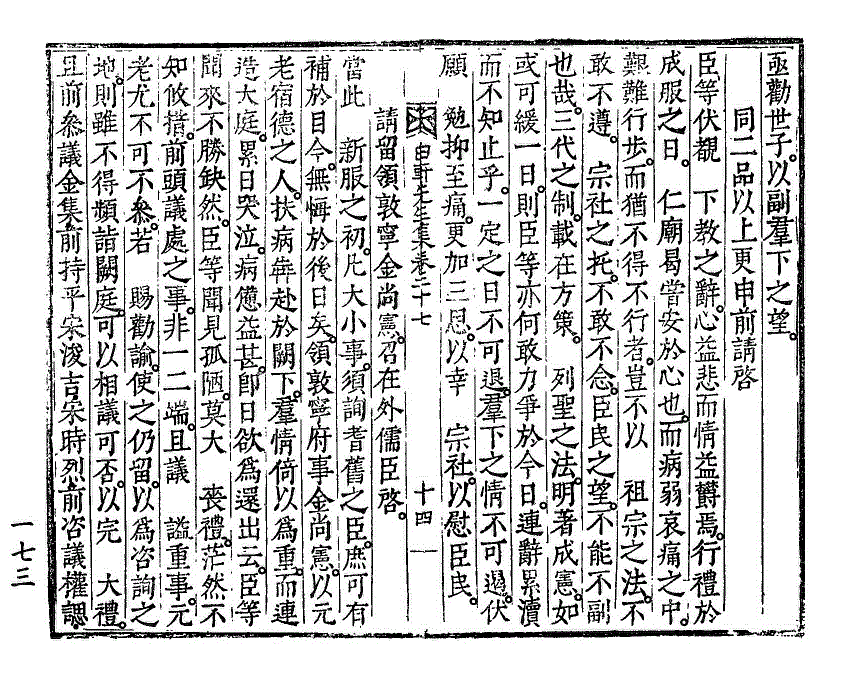 亟劝世子。以副群下之望。
亟劝世子。以副群下之望。同二品以上更申前请启
臣等伏睹 下教之辞。心益悲而情益郁焉。行礼于成服之日。 仁庙曷尝安于心也。而病弱哀痛之中。艰难行步。而犹不得不行者。岂不以 祖宗之法。不敢不遵。 宗社之托。不敢不念。臣民之望。不能不副也哉。三代之制。载在方策。 列圣之法。明著成宪。如或可缓一日。则臣等亦何敢力争于今日。连辞累渎而不知止乎。一定之日不可退。群下之情不可遏。伏愿 勉抑至痛。更加三思。以幸 宗社。以慰臣民。
请留领敦宁金尚宪。召在外儒臣启。
当此 新服之初。凡大小事。须询耆旧之臣。庶可有补于目今。无悔于后日矣。领敦宁府事金尚宪。以元老宿德之人。扶病奔赴于阙下。群情倚以为重。而连造大庭。累日哭泣。病惫益甚。即日欲为还出云。臣等闻来不胜缺然。臣等闻见孤陋。莫大 丧礼。茫然不知攸措。前头议处之事。非一二端。且议 谥重事。元老尤不可不参。若 赐劝谕。使之仍留。以为咨询之地。则虽不得频诣阙庭。可以相议可否。以完 大礼。且前参议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时烈,前咨议权諰,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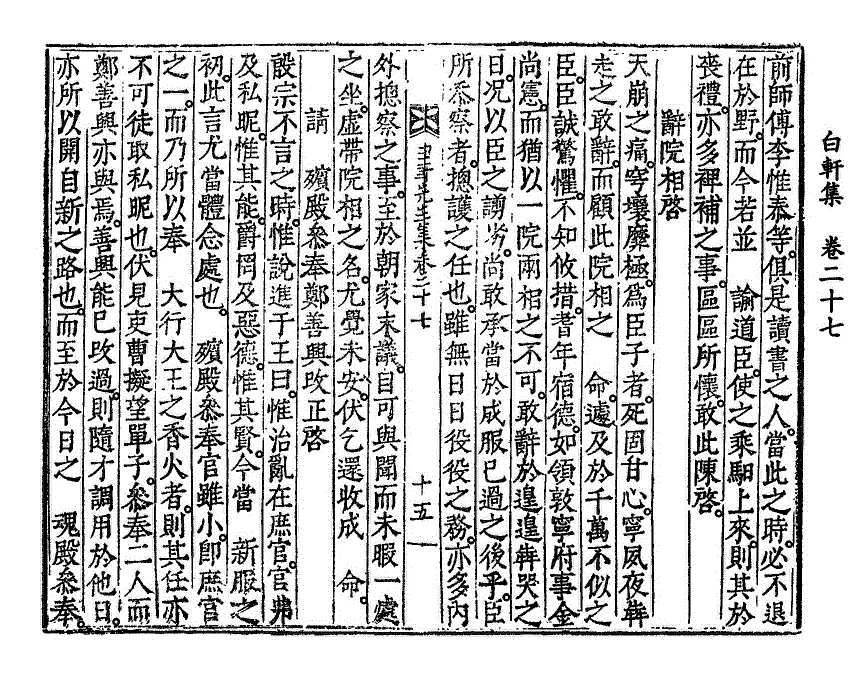 前师傅李惟泰等。俱是读书之人。当此之时。必不退在于野。而今若并 谕道臣。使之乘驲上来。则其于丧礼。亦多裨补之事。区区所怀。敢此陈启。
前师傅李惟泰等。俱是读书之人。当此之时。必不退在于野。而今若并 谕道臣。使之乘驲上来。则其于丧礼。亦多裨补之事。区区所怀。敢此陈启。辞院相启
天崩之痛。穹壤靡极。为臣子者。死固甘心。宁夙夜奔走之敢辞。而顾此院相之 命。遽及于千万不似之臣。臣诚惊惧。不知攸措。耆年宿德。如领敦宁府事金尚宪。而犹以一院两相之不可。敢辞于遑遑奔哭之日。况以臣之谫劣。尚敢承当于成服已过之后乎。臣所忝察者。总护之任也。虽无日日役役之务。亦多内外总察之事。至于朝家末议。目可与闻而未暇一处之坐。虚带院相之名。尤觉未安。伏乞还收成 命。
请 殡殿参奉郑善兴改正启
殷宗不言之时。惟说进于王曰。惟治乱在庶官。官弗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今当 新服之初。此言尤当体念处也。 殡殿参奉官虽小。即庶官之一。而乃所以奉 大行大王之香火者。则其任亦不可徒取私昵也。伏见吏曹拟望单子。参奉二人而郑善兴亦与焉。善兴能已改过。则随才调用于他日。亦所以开自新之路也。而至于今日之 魂殿参奉。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4L 页
 则汲汲然以善兴为之者。吏曹之不思甚矣。不可以官微而忽之。不可以事小而置之。臣待罪总护之任。敢此陈启。令该曹更为择拟何如。
则汲汲然以善兴为之者。吏曹之不思甚矣。不可以官微而忽之。不可以事小而置之。臣待罪总护之任。敢此陈启。令该曹更为择拟何如。长陵更审事承 命诣宾厅启
臣伏见大司宪赵翼劄辞大槩。其意以 大行大王衣冠之藏。不可不慎。术士之相。不可不广。陵所不可不更审也。而专以朱子之议山陵为主。又以金百鍊之力言其不吉为證。臣民无禄。奄遭 天崩之痛。攀号莫及。报效无地。为今日臣子尽其微诚者。惟在于慎终一事。况臣而叨受总护之仕。于此而敢不罄竭其心力。窃自附于勿之有悔者乎。其所引朱子之说。是则是矣。而第朱子所遭之时。大有异于今日。考见其议状。则绍兴五年。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复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遂中寝。朱子于是上议状。不报。其议状曰。因山之卜。累月于玆。议论纷纭。讫无定说。臣尝窃究其所以。皆缘专信台史而不广求术士。必取国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访名山。此盖悯累月之未决。慨台史之专信。欲其广求术士。博访名山之意也。今此 长陵则既非累月无定之比。又非专信台史之为。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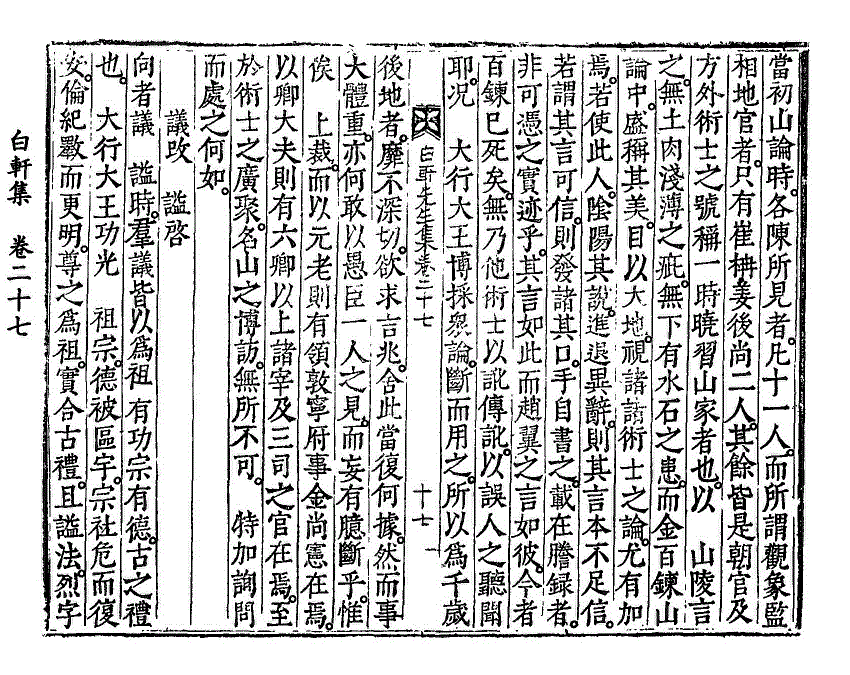 当初山论时。各陈所见者。凡十一人。而所谓观象监相地官者。只有崔楠,姜后尚二人。其馀皆是朝官及方外术士之号称一时晓习山家者也。以 山陵言之。无土肉浅薄之疵。无下有水石之患。而金百鍊山论中。盛称其美。目以大地。视诸诸术士之论。尤有加焉。若使此人。阴阳其说。进退异辞。则其言本不足信。若谓其言可信。则发诸其口。手自书之。载在誊录者。非可凭之实迹乎。其言如此而赵翼之言如彼。今者百鍊已死矣。无乃他术士以讹传讹。以误人之听闻耶。况 大行大王博采众论。断而用之。所以为千岁后地者。靡不深切。欲求吉兆。舍此当复何据。然而事大体重。亦何敢以愚臣一人之见。而妄有臆断乎。惟俟 上裁。而以元老则有领敦宁府事金尚宪在焉。以卿大夫则有六卿以上诸宰及三司之官在焉。至于术士之广聚。名山之博访。无所不可。 特加询问而处之何如。
当初山论时。各陈所见者。凡十一人。而所谓观象监相地官者。只有崔楠,姜后尚二人。其馀皆是朝官及方外术士之号称一时晓习山家者也。以 山陵言之。无土肉浅薄之疵。无下有水石之患。而金百鍊山论中。盛称其美。目以大地。视诸诸术士之论。尤有加焉。若使此人。阴阳其说。进退异辞。则其言本不足信。若谓其言可信。则发诸其口。手自书之。载在誊录者。非可凭之实迹乎。其言如此而赵翼之言如彼。今者百鍊已死矣。无乃他术士以讹传讹。以误人之听闻耶。况 大行大王博采众论。断而用之。所以为千岁后地者。靡不深切。欲求吉兆。舍此当复何据。然而事大体重。亦何敢以愚臣一人之见。而妄有臆断乎。惟俟 上裁。而以元老则有领敦宁府事金尚宪在焉。以卿大夫则有六卿以上诸宰及三司之官在焉。至于术士之广聚。名山之博访。无所不可。 特加询问而处之何如。议改 谥启
向者议 谥时。群议皆以为祖有功宗有德。古之礼也。 大行大王功光 祖宗。德被区宇。宗社危而复安。伦纪斁而更明。尊之为祖。实合古礼。且谥法。烈字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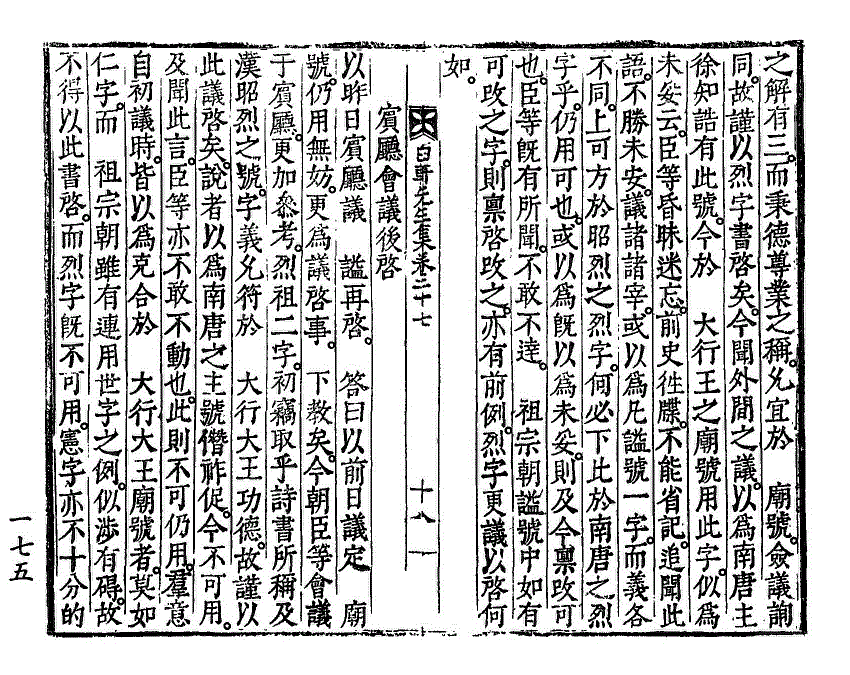 之解有三。而秉德尊业之称。允宜于 庙号。佥议询同。故谨以烈字书启矣。今闻外间之议。以为南唐主徐知诰有此号。今于 大行王之庙号用此字。似为未妥云。臣等昏昧迷忘。前史往牒。不能省记。追闻此语。不胜未安。议诸诸宰。或以为凡谥号一字。而义各不同。上可方于昭烈之烈字。何必下比于南唐之烈字乎。仍用可也。或以为既以为未妥。则及今禀改可也。臣等既有所闻。不敢不达。 祖宗朝谥号中如有可改之字。则禀启改之。亦有前例。烈字更议以启何如。
之解有三。而秉德尊业之称。允宜于 庙号。佥议询同。故谨以烈字书启矣。今闻外间之议。以为南唐主徐知诰有此号。今于 大行王之庙号用此字。似为未妥云。臣等昏昧迷忘。前史往牒。不能省记。追闻此语。不胜未安。议诸诸宰。或以为凡谥号一字。而义各不同。上可方于昭烈之烈字。何必下比于南唐之烈字乎。仍用可也。或以为既以为未妥。则及今禀改可也。臣等既有所闻。不敢不达。 祖宗朝谥号中如有可改之字。则禀启改之。亦有前例。烈字更议以启何如。宾厅会议后启
以昨日宾厅议 谥再启。 答曰以前日议定 庙号。仍用无妨。更为议启事。 下教矣。今朝臣等会议于宾厅。更加参考。烈祖二字。初窃取乎诗书所称及汉昭烈之号。字义允符于 大行大王功德。故谨以此议启矣。说者以为南唐之主号僭祚促。今不可用。及闻此言。臣等亦不敢不动也。此则不可仍用。群意自初议时。皆以为克合于 大行大王庙号者。莫如仁字。而 祖宗朝虽有连用世字之例。似涉有碍。故不得以此书启。而烈字既不可用。宪字亦不十分的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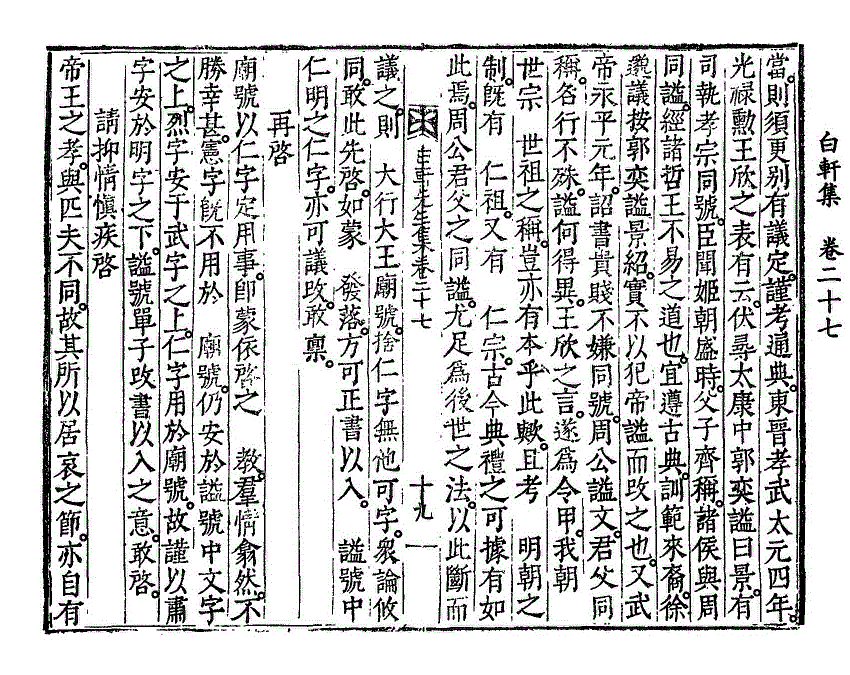 当。则须更别有议定。谨考通典。东晋孝武太元四年。光禄勋王欣之表有云。伏寻太康中郭奕谥曰景。有司执孝宗同号。臣闻姬朝盛时。父子齐称。诸侯与周同谥。经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训范来裔。徐邈议按郭奕谥景绍。实不以犯帝谥而改之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诏书贵贱不嫌同号。周公谥文。君父同称。名行不殊。谥何得异。王欣之言。遂为令甲。我朝 世宗 世祖之称。岂亦有本乎此欤。且考 明朝之制。既有 仁祖。又有 仁宗。古今典礼之可据有如此焉。周公君父之同谥。尤足为后世之法。以此断而议之。则 大行大王庙号。舍仁字无他可字。众论攸同。敢此先启。如蒙 发落。方可正书以入。 谥号中仁明之仁字。亦可议改。敢禀。
当。则须更别有议定。谨考通典。东晋孝武太元四年。光禄勋王欣之表有云。伏寻太康中郭奕谥曰景。有司执孝宗同号。臣闻姬朝盛时。父子齐称。诸侯与周同谥。经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训范来裔。徐邈议按郭奕谥景绍。实不以犯帝谥而改之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诏书贵贱不嫌同号。周公谥文。君父同称。名行不殊。谥何得异。王欣之言。遂为令甲。我朝 世宗 世祖之称。岂亦有本乎此欤。且考 明朝之制。既有 仁祖。又有 仁宗。古今典礼之可据有如此焉。周公君父之同谥。尤足为后世之法。以此断而议之。则 大行大王庙号。舍仁字无他可字。众论攸同。敢此先启。如蒙 发落。方可正书以入。 谥号中仁明之仁字。亦可议改。敢禀。宾厅会议后启[再启]
庙号以仁字定用事。即蒙依启之 教。群情翕然。不胜幸甚。宪字既不用于 庙号。仍安于谥号中文字之上。烈字安于武字之上。仁字用于庙号。故谨以肃字安于明字之下。谥号单子改书以入之意。敢启。
请抑情慎疾启
帝王之孝。与匹夫不同。故其所以居哀之节。亦自有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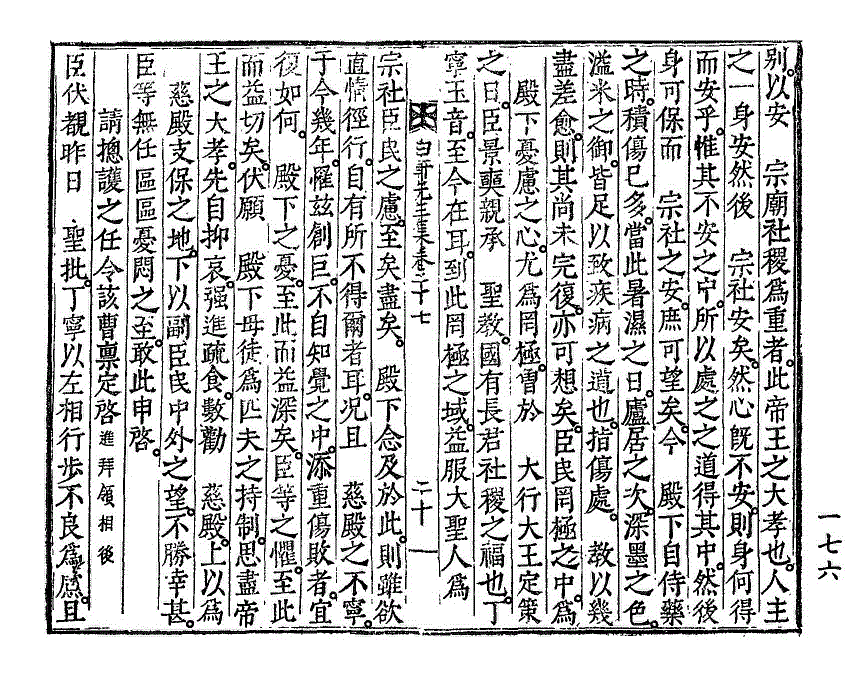 别。以安 宗庙社稷为重者。此帝王之大孝也。人主之一身安然后 宗社安矣。然心既不安。则身何得而安乎。惟其不安之中。所以处之之道得其中。然后身可保而 宗社之安。庶可望矣。今 殿下自侍药之时。积伤已多。当此暑湿之日。庐居之次。深墨之色。溢米之御。皆足以致疾病之道也。指伤处。 教以几尽差愈。则其尚未完复。亦可想矣。臣民罔极之中。为 殿下忧虑之心。尤为罔极。曾于 大行大王定策之日。臣景奭亲承 圣教。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丁宁玉音。至今在耳。到此罔极之域。益服大圣人为 宗社臣民之虑。至矣尽矣。 殿下念及于此。则虽欲直情径行。自有所不得尔者耳。况且 慈殿之不宁。于今几年。罹玆创巨。不自知觉之中。添重伤败者。宜复如何。 殿下之忧。至此而益深矣。臣等之惧。至此而益切矣。伏愿 殿下毋徒为匹夫之持制。思尽帝王之大孝。先自抑哀。强进疏食。数劝 慈殿。上以为 慈殿支保之地。下以副臣民中外之望。不胜幸甚。臣等无任区区忧闷之至。敢此申启。
别。以安 宗庙社稷为重者。此帝王之大孝也。人主之一身安然后 宗社安矣。然心既不安。则身何得而安乎。惟其不安之中。所以处之之道得其中。然后身可保而 宗社之安。庶可望矣。今 殿下自侍药之时。积伤已多。当此暑湿之日。庐居之次。深墨之色。溢米之御。皆足以致疾病之道也。指伤处。 教以几尽差愈。则其尚未完复。亦可想矣。臣民罔极之中。为 殿下忧虑之心。尤为罔极。曾于 大行大王定策之日。臣景奭亲承 圣教。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丁宁玉音。至今在耳。到此罔极之域。益服大圣人为 宗社臣民之虑。至矣尽矣。 殿下念及于此。则虽欲直情径行。自有所不得尔者耳。况且 慈殿之不宁。于今几年。罹玆创巨。不自知觉之中。添重伤败者。宜复如何。 殿下之忧。至此而益深矣。臣等之惧。至此而益切矣。伏愿 殿下毋徒为匹夫之持制。思尽帝王之大孝。先自抑哀。强进疏食。数劝 慈殿。上以为 慈殿支保之地。下以副臣民中外之望。不胜幸甚。臣等无任区区忧闷之至。敢此申启。请总护之任令该曹禀定启(进拜领相后)
臣伏睹昨日 圣批。丁宁以左相行步不良为虑。且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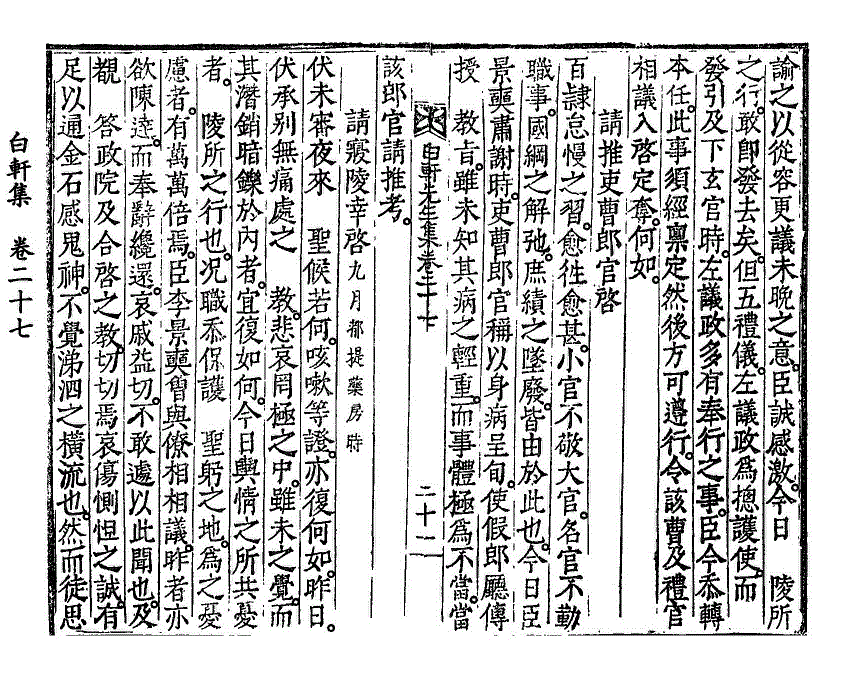 谕之以从容更议未晚之意。臣诚感激。今日 陵所之行。敢即发去矣。但五礼仪。左议政为总护使。而 发引及下玄宫时。左议政多有奉行之事。臣今忝转本任。此事须经禀定然后方可遵行。令该曹及礼官相议入启定夺。何如。
谕之以从容更议未晚之意。臣诚感激。今日 陵所之行。敢即发去矣。但五礼仪。左议政为总护使。而 发引及下玄宫时。左议政多有奉行之事。臣今忝转本任。此事须经禀定然后方可遵行。令该曹及礼官相议入启定夺。何如。请推吏曹郎官启
百隶怠慢之习。愈往愈甚。小官不敬大官。名官不勤职事。国纲之解弛。庶绩之坠废。皆由于此也。今日臣景奭肃谢时。吏曹郎官称以身病呈旬。使假郎厅传授 教旨。虽未知其病之轻重。而事体极为不当。当该郎官请推考。
请寝陵幸启(九月都提药房时)
伏未审夜来 圣候若何。咳嗽等證。亦复何如。昨日。伏承别无痛处之 教。悲哀罔极之中。虽未之觉。而其潜销暗铄于内者。宜复如何。今日舆情之所共忧者。 陵所之行也。况职忝保护 圣躬之地。为之忧虑者。有万万倍焉。臣李景奭曾与僚相相议。昨者亦欲陈达。而奉辞才还。哀戚益切。不敢遽以此闻也。及睹 答政院及合启之教。切切焉哀伤恻怛之诚。有足以通金石感鬼神。不觉涕泗之横流也。然而徒思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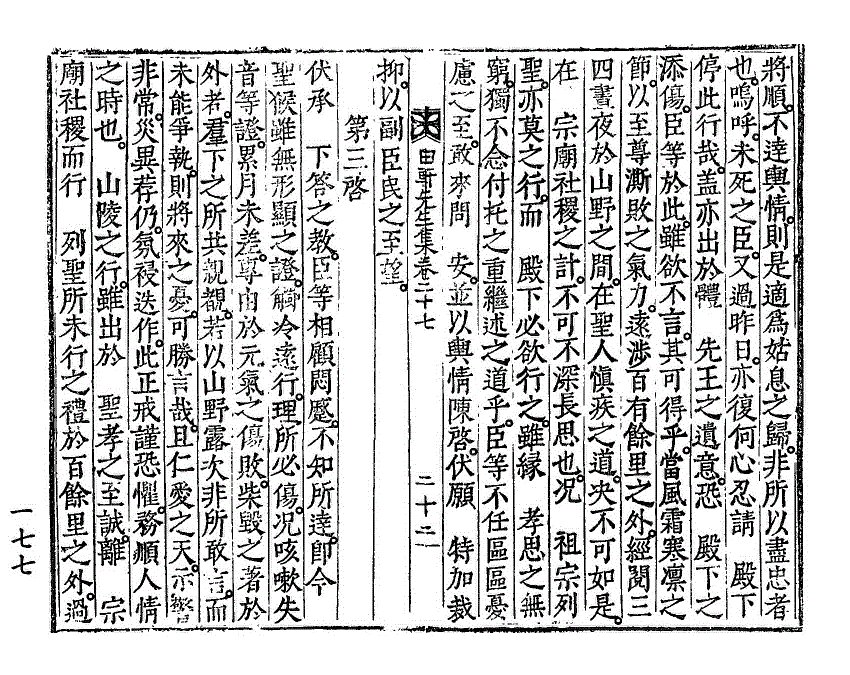 将顺。不达舆情。则是适为姑息之归。非所以尽忠者也。呜呼。未死之臣。又过昨日。亦复何心忍请 殿下停此行哉。盖亦出于体 先王之遗意。恐 殿下之添伤。臣等于此。虽欲不言。其可得乎。当风霜寒凛之节。以至尊澌败之气力。远涉百有馀里之外。经阅三四昼夜于山野之间。在圣人慎疾之道。决不可如是。在 宗庙社稷之计。不可不深长思也。况 祖宗列圣。亦莫之行。而 殿下必欲行之。虽缘 孝思之无穷。独不念付托之重继述之道乎。臣等不任区区忧虑之至。敢来问 安。并以舆情陈启。伏愿 特加裁抑。以副臣民之至望。
将顺。不达舆情。则是适为姑息之归。非所以尽忠者也。呜呼。未死之臣。又过昨日。亦复何心忍请 殿下停此行哉。盖亦出于体 先王之遗意。恐 殿下之添伤。臣等于此。虽欲不言。其可得乎。当风霜寒凛之节。以至尊澌败之气力。远涉百有馀里之外。经阅三四昼夜于山野之间。在圣人慎疾之道。决不可如是。在 宗庙社稷之计。不可不深长思也。况 祖宗列圣。亦莫之行。而 殿下必欲行之。虽缘 孝思之无穷。独不念付托之重继述之道乎。臣等不任区区忧虑之至。敢来问 安。并以舆情陈启。伏愿 特加裁抑。以副臣民之至望。请寝陵幸启(九月都提药房时)[第三启]
伏承 下答之教。臣等相顾闷蹙。不知所达。即今 圣候虽无形显之證。触冷远行。理所必伤。况咳嗽失音等證。累月未差。专由于元气之伤败。柴毁之著于外者。群下之所共亲睹。若以山野露次非所敢言。而未能争执。则将来之忧。可胜言哉。且仁爱之天。示警非常。灾异荐仍。氛祲迭作。此正戒谨恐惧。务顺人情之时也。 山陵之行。虽出于 圣孝之至诚。离 宗庙社稷而行 列圣所未行之礼于百馀里之外。过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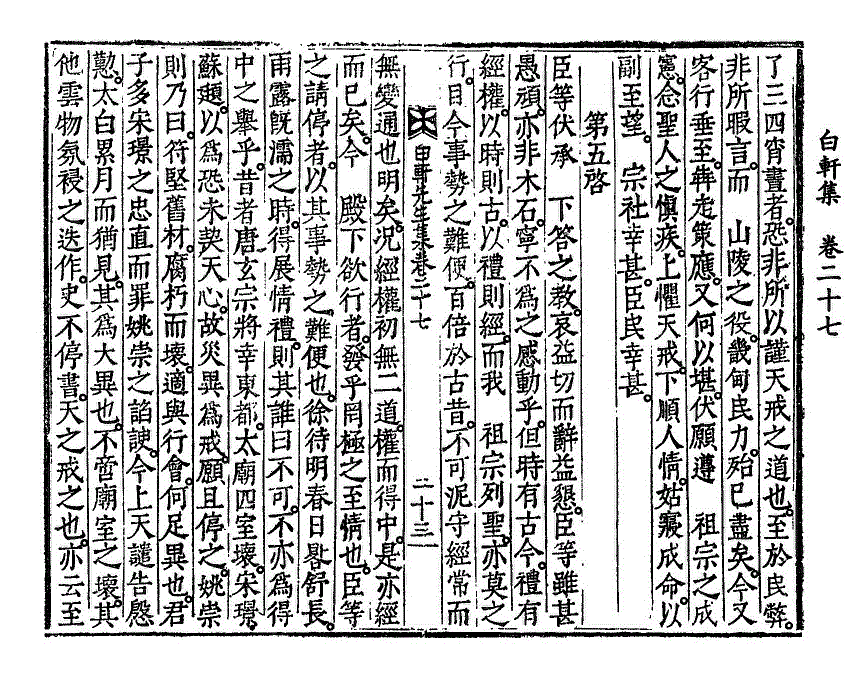 了三四宵昼者。恐非所以谨天戒之道也。至于民弊。非所暇言。而 山陵之役。畿甸民力。殆已尽矣。今又客行垂至。奔走策应。又何以堪。伏愿遵 祖宗之成宪。念圣人之慎疾。上惧天戒。下顺人情。姑寝成命。以副至望。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了三四宵昼者。恐非所以谨天戒之道也。至于民弊。非所暇言。而 山陵之役。畿甸民力。殆已尽矣。今又客行垂至。奔走策应。又何以堪。伏愿遵 祖宗之成宪。念圣人之慎疾。上惧天戒。下顺人情。姑寝成命。以副至望。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请寝陵幸启(九月都提药房时)[第五启]
臣等伏承 下答之教。哀益切而辞益恳。臣等虽甚愚顽。亦非木石。宁不为之感动乎。但时有古今。礼有经权。以时则古。以礼则经。而我 祖宗列圣。亦莫之行。目今事势之难便。百倍于古昔。不可泥守经常而无变通也明矣。况经权初无二道。权而得中。是亦经而已矣。今 殿下欲行者。发乎罔极之至情也。臣等之请停者。以其事势之难便也。徐待明春日晷舒长。雨露既濡之时。得展情礼。则其谁曰不可。不亦为得中之举乎。昔者唐玄宗将幸东都。太庙四室坏。宋璟,苏颋。以为恐未契天心。故灾异为戒。愿且停之。姚崇则乃曰。符坚旧材。腐朽而坏。适与行会。何足异也。君子多宋璟之忠直而罪姚崇之谄谀。今上天谴告慇勤。太白累月而犹见。其为大异也。不啻庙室之坏。其他云物氛祲之迭作。史不停书。天之戒之也。亦云至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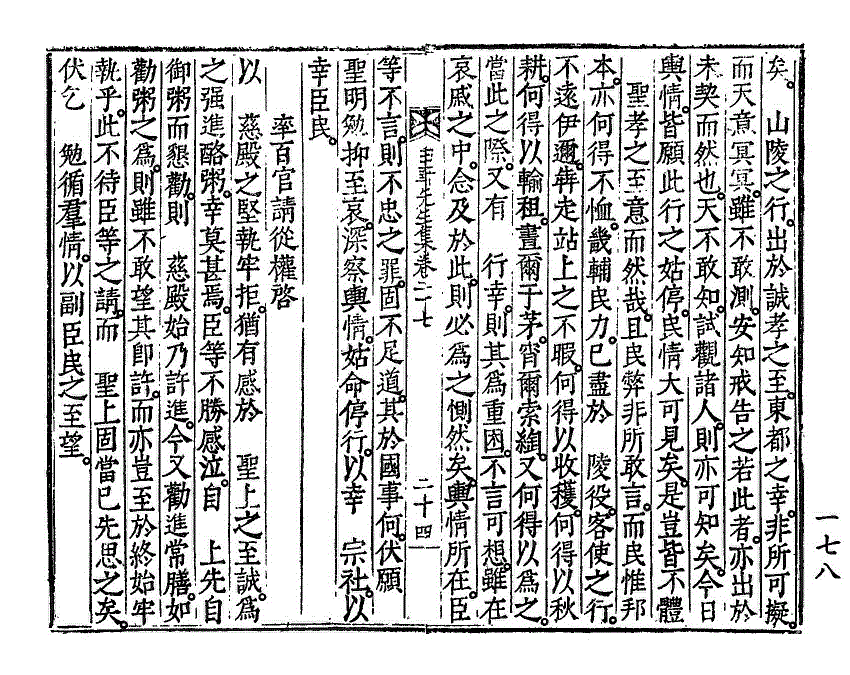 矣。 山陵之行。出于诚孝之至。东都之幸。非所可拟。而天意冥冥。虽不敢测。安知戒告之若此者。亦出于未契而然也。天不敢知。试观诸人。则亦可知矣。今日舆情。皆愿此行之姑停。民情大可见矣。是岂皆不体 圣孝之至意而然哉。且民弊非所敢言。而民惟邦本。亦何得不恤。畿辅民力。已尽于 陵役。客使之行。不远伊迩。奔走站上之不暇。何得以收穫。何得以秋耕。何得以输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又何得以为之。当此之际。又有 行幸。则其为重困。不言可想。虽在哀戚之中。念及于此。则必为之恻然矣。舆情所在。臣等不言。则不忠之罪。固不足道。其于国事何。伏愿 圣明勉抑至哀。深察舆情。姑命停行。以幸 宗社。以幸臣民。
矣。 山陵之行。出于诚孝之至。东都之幸。非所可拟。而天意冥冥。虽不敢测。安知戒告之若此者。亦出于未契而然也。天不敢知。试观诸人。则亦可知矣。今日舆情。皆愿此行之姑停。民情大可见矣。是岂皆不体 圣孝之至意而然哉。且民弊非所敢言。而民惟邦本。亦何得不恤。畿辅民力。已尽于 陵役。客使之行。不远伊迩。奔走站上之不暇。何得以收穫。何得以秋耕。何得以输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又何得以为之。当此之际。又有 行幸。则其为重困。不言可想。虽在哀戚之中。念及于此。则必为之恻然矣。舆情所在。臣等不言。则不忠之罪。固不足道。其于国事何。伏愿 圣明勉抑至哀。深察舆情。姑命停行。以幸 宗社。以幸臣民。率百官请从权启
以 慈殿之坚执牢拒。犹有感于 圣上之至诚。为之强进酪粥。幸莫甚焉。臣等不胜感泣。自 上先自御粥而恳劝。则 慈殿始乃许进。今又劝进常膳。如劝粥之为。则虽不敢望其即许。而亦岂至于终始牢执乎。此不待臣等之请。而 圣上固当已先思之矣。伏乞 勉循群情。以副臣民之至望。
慈殿率百官口传启
臣等伏閤仰吁。至下臣子不忍闻之 教。何牢拒之太过也。臣等请以古事仰达。宋英宗时。大臣韩琦亲白太后曰。上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其责。太后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今 主上之身。若未调护。 慈殿亦不得辞其责。 殿下之心。何得不为之更切也。伏愿 亟徇群情。特许权制。以保 圣上之躬。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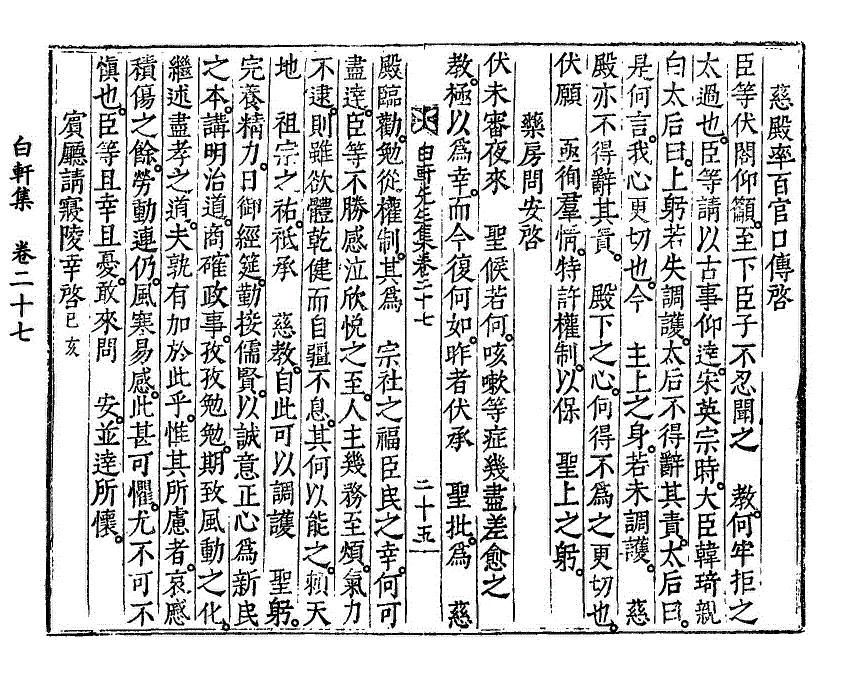 药房问安启
药房问安启伏未审夜来 圣候若何。咳嗽等症几尽差愈之 教。极以为幸。而今复何如。昨者伏承 圣批。为 慈殿临劝。勉从权制。其为 宗社之福臣民之幸。何可尽达。臣等不胜感泣欣悦之至。人主几务至烦。气力不逮。则虽欲体乾健而自彊不息。其何以能之。赖天地 祖宗之祐。祗承 慈教。自此可以调护 圣躬。完养精力。日御经筵。勤接儒贤。以诚意正心为新民之本。讲明治道。商确政事。孜孜勉勉。期致风动之化。继述尽孝之道。夫孰有加于此乎。惟其所虑者。哀戚积伤之馀。劳动连仍。风寒易感。此甚可惧。尤不可不慎也。臣等且幸且忧。敢来问 安。并达所怀。
宾厅请寝陵幸启(己亥)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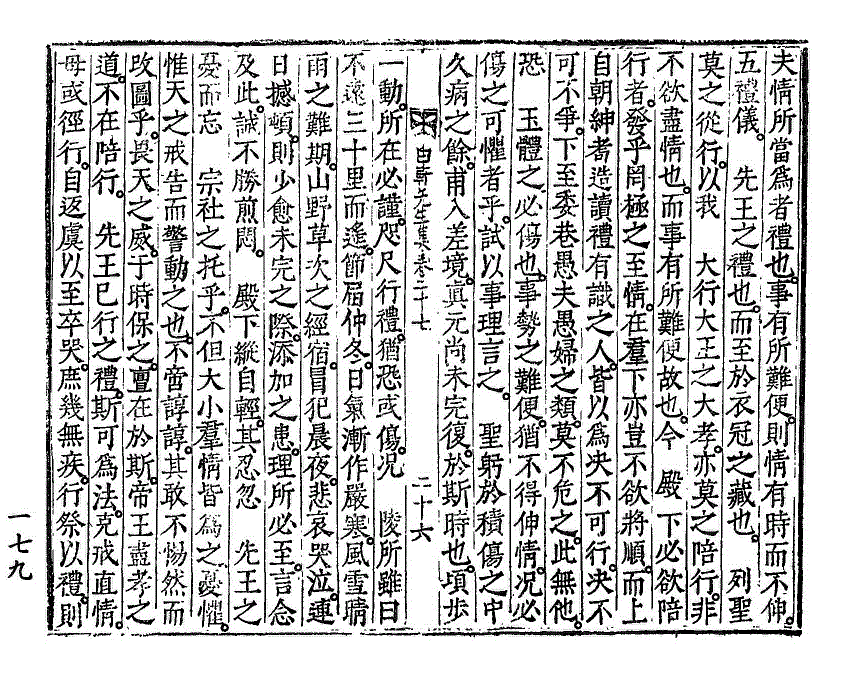 夫情所当为者礼也。事有所难便。则情有时而不伸。五礼仪。 先王之礼也。而至于衣冠之藏也。 列圣莫之从行。以我 大行大王之大孝。亦莫之陪行。非不欲尽情也。而事有所难便故也。今 殿下必欲陪行者。发乎罔极之至情。在群下亦岂不欲将顺。而上自朝绅耇造读礼有识之人。皆以为决不可行。决不可不争。下至委巷愚夫愚妇之类。莫不危之。此无他。恐 玉体之必伤也。事势之难便。犹不得伸情。况必伤之可惧者乎。试以事理言之。 圣躬于积伤之中久病之馀。甫入差境。真元尚未完复。于斯时也。顷步一动。所在必谨。咫尺行礼。犹恐或伤。况 陵所虽曰不远三十里而遥。节届仲冬。日气渐作严寒。风雪晴雨之难期。山野草次之经宿。冒犯晨夜。悲哀哭泣。连日撼顿。则少愈未完之际。添加之患。理所必至。言念及此。诚不胜煎闷。 殿下纵自轻。其忍忽 先王之忧而忘 宗社之托乎。不但大小群情皆为之忧惧。惟天之戒告而警动之也。不啻谆谆。其敢不惕然而改图乎。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亶在于斯。帝王尽孝之道。不在陪行。 先王已行之礼。斯可为法。克戒直情。毋或径行。自返虞以至卒哭。庶几无疾。行祭以礼。则
夫情所当为者礼也。事有所难便。则情有时而不伸。五礼仪。 先王之礼也。而至于衣冠之藏也。 列圣莫之从行。以我 大行大王之大孝。亦莫之陪行。非不欲尽情也。而事有所难便故也。今 殿下必欲陪行者。发乎罔极之至情。在群下亦岂不欲将顺。而上自朝绅耇造读礼有识之人。皆以为决不可行。决不可不争。下至委巷愚夫愚妇之类。莫不危之。此无他。恐 玉体之必伤也。事势之难便。犹不得伸情。况必伤之可惧者乎。试以事理言之。 圣躬于积伤之中久病之馀。甫入差境。真元尚未完复。于斯时也。顷步一动。所在必谨。咫尺行礼。犹恐或伤。况 陵所虽曰不远三十里而遥。节届仲冬。日气渐作严寒。风雪晴雨之难期。山野草次之经宿。冒犯晨夜。悲哀哭泣。连日撼顿。则少愈未完之际。添加之患。理所必至。言念及此。诚不胜煎闷。 殿下纵自轻。其忍忽 先王之忧而忘 宗社之托乎。不但大小群情皆为之忧惧。惟天之戒告而警动之也。不啻谆谆。其敢不惕然而改图乎。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亶在于斯。帝王尽孝之道。不在陪行。 先王已行之礼。斯可为法。克戒直情。毋或径行。自返虞以至卒哭。庶几无疾。行祭以礼。则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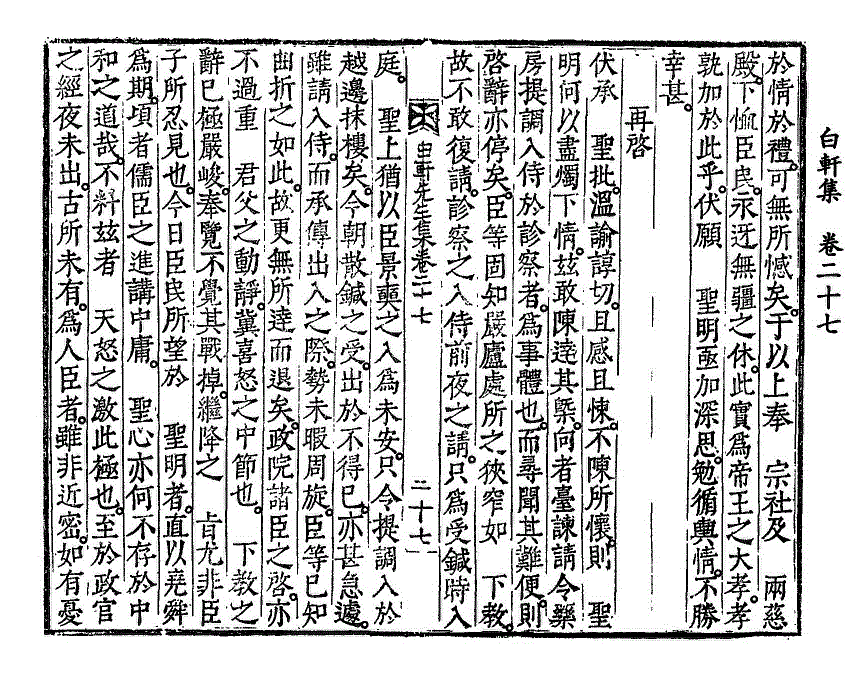 于情于礼。可无所憾矣。于以上奉 宗社及 两慈殿。下恤臣民。永迓无疆之休。此实为帝王之大孝。孝孰加于此乎。伏愿 圣明亟加深思。勉循舆情。不胜幸甚。
于情于礼。可无所憾矣。于以上奉 宗社及 两慈殿。下恤臣民。永迓无疆之休。此实为帝王之大孝。孝孰加于此乎。伏愿 圣明亟加深思。勉循舆情。不胜幸甚。宾厅请寝陵幸启(己亥)[再启]
伏承 圣批。温谕谆切。且感且悚。不陈所怀。则 圣明何以尽烛下情。玆敢陈达其槩。向者台谏请令药房提调入侍于诊察者。为事体也。而寻闻其难便。则启辞亦停矣。臣等固知严庐处所之狭窄如 下教。故不敢复请。诊察之入侍前夜之请。只为受针时入庭。 圣上犹以臣景奭之入为未安。只令提调入于越边抹楼矣。今朝散针之受。出于不得已。亦甚急遽。虽请入侍。而承传出入之际。势未暇周旋。臣等已知曲折之如此。故更无所达而退矣。政院诸臣之启。亦不过重 君父之动静。冀喜怒之中节也。 下教之辞已极严峻。奉览不觉其战掉。继降之 旨尤非臣子所忍见也。今日臣民所望于 圣明者。直以尧舜为期。顷者儒臣之进讲中庸。 圣心亦何不存于中和之道哉。不料玆者 天怒之激此极也。至于政官之经夜未出。古所未有。为人臣者。虽非近密。如有忧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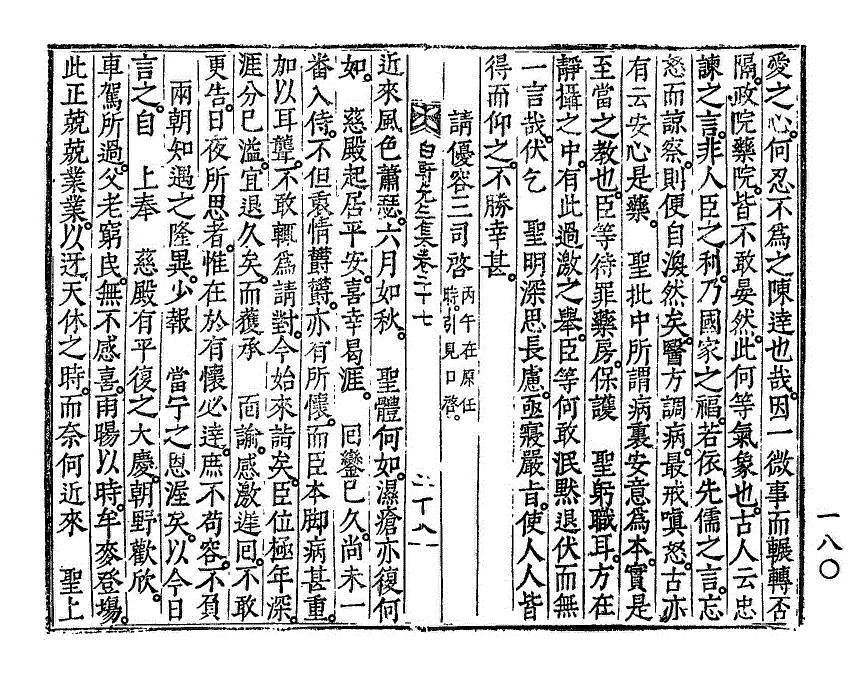 爱之心。何忍不为之陈达也哉。因一微事而辗辅否隔。政院药院。皆不敢晏然。此何等气象也。古人云忠谏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若依先儒之言。忘怒而谅察。则便自涣然矣。医方调病。最戒嗔怒。古亦有云安心是药。 圣批中所谓病里安意为本。实是至当之教也。臣等待罪药房。保护 圣躬职耳。方在静摄之中。有此过激之举。臣等何敢泯默退伏而无一言哉。伏乞 圣明深思长虑。亟寝严旨。使人人皆得而仰之。不胜幸甚。
爱之心。何忍不为之陈达也哉。因一微事而辗辅否隔。政院药院。皆不敢晏然。此何等气象也。古人云忠谏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若依先儒之言。忘怒而谅察。则便自涣然矣。医方调病。最戒嗔怒。古亦有云安心是药。 圣批中所谓病里安意为本。实是至当之教也。臣等待罪药房。保护 圣躬职耳。方在静摄之中。有此过激之举。臣等何敢泯默退伏而无一言哉。伏乞 圣明深思长虑。亟寝严旨。使人人皆得而仰之。不胜幸甚。请优容三司启(丙午在原任时。引见口启。)
近来风色萧瑟。六月如秋。 圣体何如。湿疮亦复何如。 慈殿起居平安。喜幸曷涯。 回銮已久。尚未一番入侍。不但衷情郁郁。亦有所怀。而臣本脚病甚重。加以耳聋。不敢辄为请对。今始来诣矣。臣位极年深。涯分已溢。宜退久矣。而获承 面谕。感激迟回。不敢更告。日夜所思者。惟在于有怀必达。庶不苟容。不负 两朝知遇之隆异。少报 当宁之恩渥矣。以今日言之。自 上奉 慈殿有平复之大庆。朝野欢欣。 车驾所过。父老穷民。无不感喜。雨旸以时。牟麦登场。此正兢兢业业。以迓天休之时。而奈何近来 圣上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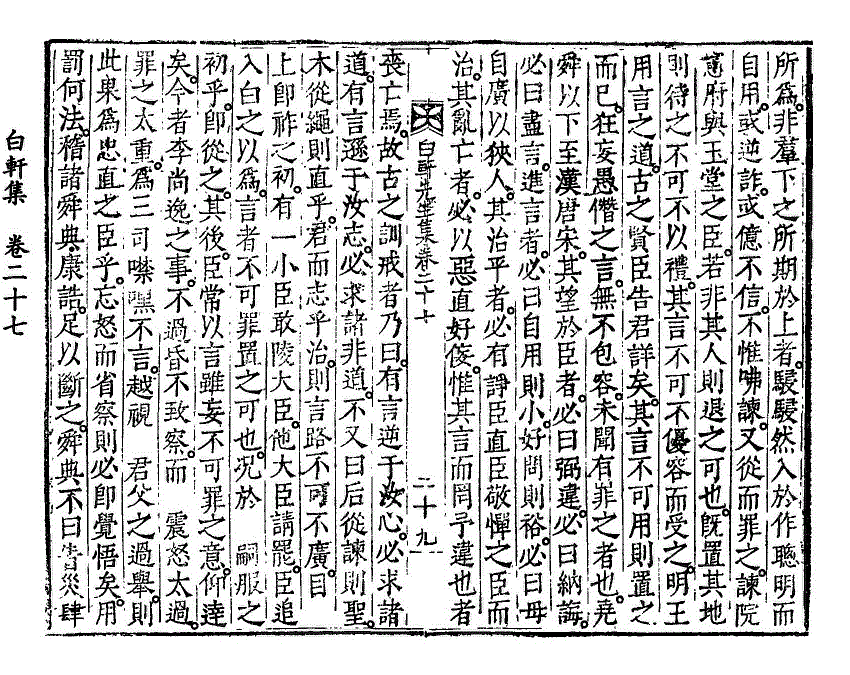 所为。非群下之所期于上者。骎骎然入于作聪明而自用。或逆诈。或亿不信。不惟咈谏。又从而罪之。谏院宪府与玉堂之臣。若非其人则退之可也。既置其地则待之不可不以礼。其言不可不优容而受之。明王用言之道。古之贤臣告君详矣。其言不可用则置之而已。狂妄愚僭之言。无不包容。未闻有罪之者也。尧舜以下至汉唐宋。其望于臣者。必曰弼违。必曰纳诲。必曰尽言。进言者。必曰自用则小。好问则裕。必曰毋自广以狭人。其治平者。必有诤臣直臣敬惮之臣而治。其乱亡者。必以恶直好佞。惟其言而罔予违也者丧亡焉。故古之训戒者乃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不又曰后从谏则圣。木从绳则直乎。君而志乎治。则言路不可不广。目 上即祚之初。有一小臣敢陵大臣。他大臣请罢。臣追入白之以为。言者不可罪置之可也。况于 嗣服之初乎。即从之。其后。臣常以言虽妄不可罪之意。仰达矣。今者李尚逸之事。不过昏不致察。而 震怒太过。罪之太重。为三司噤嘿不言。越视 君父之过举。则此果为忠直之臣乎。忘怒而省察则必即觉悟矣。用罚何法。稽诸舜典,康诰。足以断之。舜典不曰眚灾肆
所为。非群下之所期于上者。骎骎然入于作聪明而自用。或逆诈。或亿不信。不惟咈谏。又从而罪之。谏院宪府与玉堂之臣。若非其人则退之可也。既置其地则待之不可不以礼。其言不可不优容而受之。明王用言之道。古之贤臣告君详矣。其言不可用则置之而已。狂妄愚僭之言。无不包容。未闻有罪之者也。尧舜以下至汉唐宋。其望于臣者。必曰弼违。必曰纳诲。必曰尽言。进言者。必曰自用则小。好问则裕。必曰毋自广以狭人。其治平者。必有诤臣直臣敬惮之臣而治。其乱亡者。必以恶直好佞。惟其言而罔予违也者丧亡焉。故古之训戒者乃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不又曰后从谏则圣。木从绳则直乎。君而志乎治。则言路不可不广。目 上即祚之初。有一小臣敢陵大臣。他大臣请罢。臣追入白之以为。言者不可罪置之可也。况于 嗣服之初乎。即从之。其后。臣常以言虽妄不可罪之意。仰达矣。今者李尚逸之事。不过昏不致察。而 震怒太过。罪之太重。为三司噤嘿不言。越视 君父之过举。则此果为忠直之臣乎。忘怒而省察则必即觉悟矣。用罚何法。稽诸舜典,康诰。足以断之。舜典不曰眚灾肆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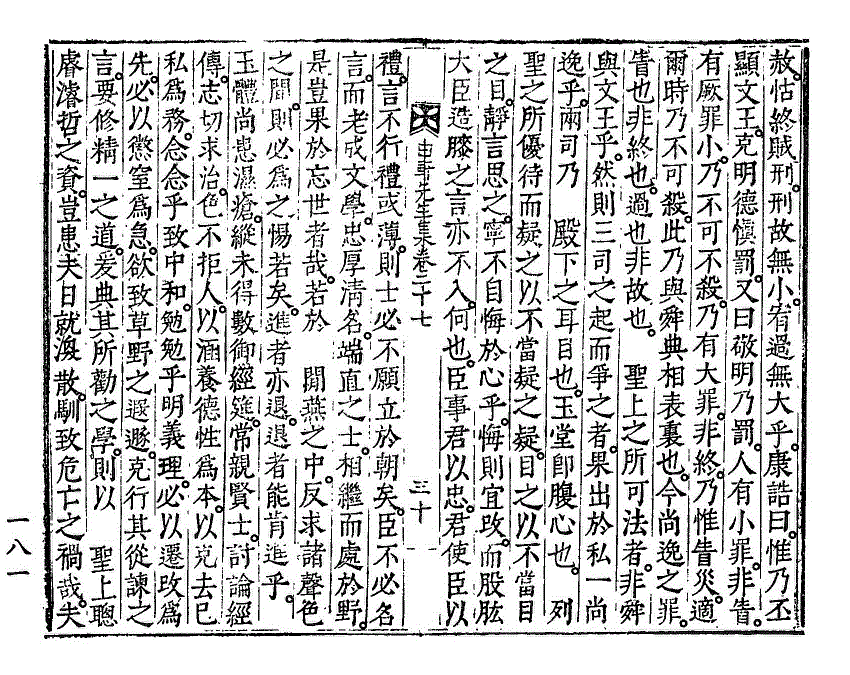 赦。怙终贼刑。刑故无小。宥过无大乎。康诰曰。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又曰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时乃不可杀。此乃与舜典相表里也。今尚逸之罪。眚也非终也。过也非故也。 圣上之所可法者。非舜与文王乎。然则三司之起而争之者。果出于私一尚逸乎。两司乃 殿下之耳目也。玉堂即腹心也。 列圣之所优待而疑之以不当疑之疑。目之以不当目之目。静言思之。宁不自悔于心乎。悔则宜改。而股肱大臣造膝之言亦不入。何也。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言不行礼或薄。则士必不愿立于朝矣。臣不必名言。而老成文学。忠厚清名。端直之士。相继而处于野。是岂果于忘世者哉。若于 閒燕之中。反求诸声色之间。则必为之惕若矣。进者亦退。退者能肯进乎。 玉体尚患湿疮。纵未得数御经筵。常亲贤士。讨论经传。志切求治。色不拒人。以涵养德性为本。以克去己私为务。念念乎致中和。勉勉乎明义理。必以迁改为先。必以惩窒为急。欲致草野之遐遁。克行其从谏之言。要修精一之道。爰典其所劝之学。则以 圣上聪睿浚哲之资。岂患夫日就涣散。驯致危亡之祸哉。夫
赦。怙终贼刑。刑故无小。宥过无大乎。康诰曰。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又曰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时乃不可杀。此乃与舜典相表里也。今尚逸之罪。眚也非终也。过也非故也。 圣上之所可法者。非舜与文王乎。然则三司之起而争之者。果出于私一尚逸乎。两司乃 殿下之耳目也。玉堂即腹心也。 列圣之所优待而疑之以不当疑之疑。目之以不当目之目。静言思之。宁不自悔于心乎。悔则宜改。而股肱大臣造膝之言亦不入。何也。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言不行礼或薄。则士必不愿立于朝矣。臣不必名言。而老成文学。忠厚清名。端直之士。相继而处于野。是岂果于忘世者哉。若于 閒燕之中。反求诸声色之间。则必为之惕若矣。进者亦退。退者能肯进乎。 玉体尚患湿疮。纵未得数御经筵。常亲贤士。讨论经传。志切求治。色不拒人。以涵养德性为本。以克去己私为务。念念乎致中和。勉勉乎明义理。必以迁改为先。必以惩窒为急。欲致草野之遐遁。克行其从谏之言。要修精一之道。爰典其所劝之学。则以 圣上聪睿浚哲之资。岂患夫日就涣散。驯致危亡之祸哉。夫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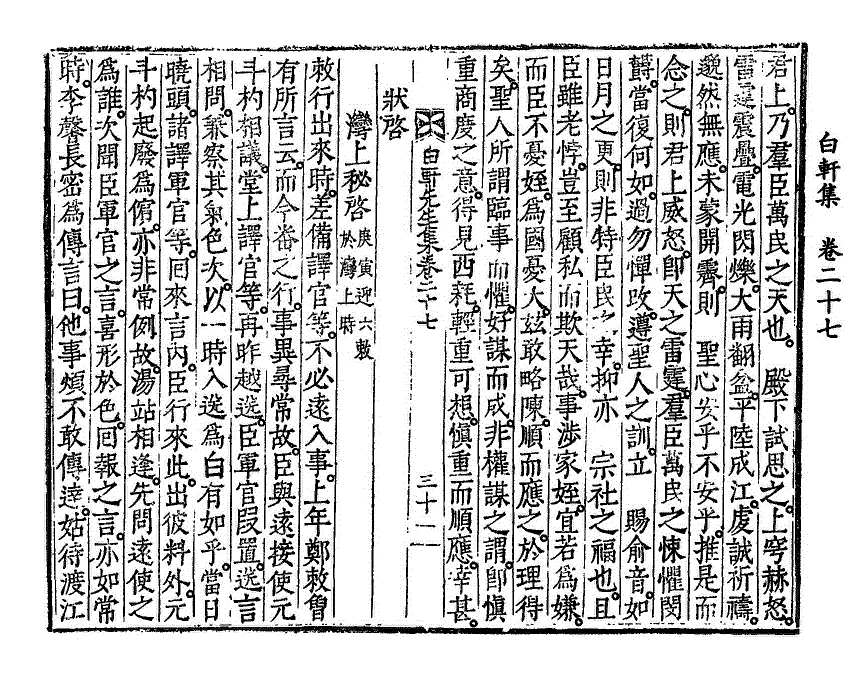 君上。乃群臣万民之天也。 殿下试思之。上穹赫怒。雷霆震叠。电光闪烁。大雨翻盆。平陆成江。虔诚祈祷。邈然无应。未蒙开霁。则 圣心安乎不安乎。推是而念之。则君上威怒。即天之雷霆。群臣万民之悚惧闵郁。当复何如。过勿惮改。遵圣人之训。立 赐俞音。如日月之更。则非特臣民之幸。抑亦 宗社之福也。且臣虽老悖。岂至顾私而欺天哉。事涉家侄。宜若为嫌。而臣不忧侄。为国忧大。玆敢略陈。顺而应之。于理得矣。圣人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非权谋之谓。即慎重商度之意。得见西耗。轻重可想。慎重而顺应。幸甚。
君上。乃群臣万民之天也。 殿下试思之。上穹赫怒。雷霆震叠。电光闪烁。大雨翻盆。平陆成江。虔诚祈祷。邈然无应。未蒙开霁。则 圣心安乎不安乎。推是而念之。则君上威怒。即天之雷霆。群臣万民之悚惧闵郁。当复何如。过勿惮改。遵圣人之训。立 赐俞音。如日月之更。则非特臣民之幸。抑亦 宗社之福也。且臣虽老悖。岂至顾私而欺天哉。事涉家侄。宜若为嫌。而臣不忧侄。为国忧大。玆敢略陈。顺而应之。于理得矣。圣人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非权谋之谓。即慎重商度之意。得见西耗。轻重可想。慎重而顺应。幸甚。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状启
湾上秘启(庚寅迎六敕于湾上时)
敕行出来时。差备译官等。不必远入事。上年郑敕曾有所言云。而今番之行。事异寻常故。臣与远接使元斗杓相议。堂上译官等。再昨越送。臣军官段置。送言相问。兼察其气色次。以一时入送为白有如乎。当日晓头。诸译军官等。回来言内。臣行来此。出彼料外。元斗杓起废为傧。亦非常例故。汤站相逢。先问远使之为谁。次闻臣军官之言。喜形于色。回报之言。亦如常时。李馨长密为传言曰。他事烦不敢传达。姑待渡江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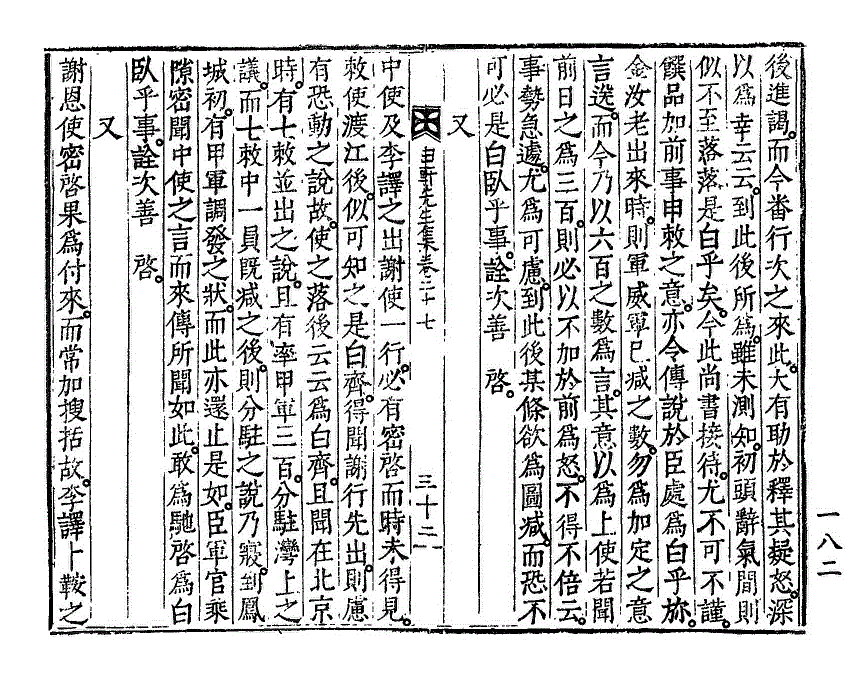 后进谒。而今番行次之来此。大有助于释其疑怒。深以为幸云云。到此后所为。虽未测知。初头辞气间则似不至落落是白乎矣。今此尚书接待。尤不可不谨。馔品加前事申敕之意。亦令传说于臣处为白乎旀。金汝老出来时。则军威军已减之数。勿为加定之意言送。而今乃以六百之数为言。其意以为上使若闻前日之为三百。则必以不加于前为怒。不得不倍云。事势急遽。尤为可虑。到此后某条欲为图减。而恐不可必是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
后进谒。而今番行次之来此。大有助于释其疑怒。深以为幸云云。到此后所为。虽未测知。初头辞气间则似不至落落是白乎矣。今此尚书接待。尤不可不谨。馔品加前事申敕之意。亦令传说于臣处为白乎旀。金汝老出来时。则军威军已减之数。勿为加定之意言送。而今乃以六百之数为言。其意以为上使若闻前日之为三百。则必以不加于前为怒。不得不倍云。事势急遽。尤为可虑。到此后某条欲为图减。而恐不可必是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湾上秘启(庚寅迎六敕于湾上时)]
中使及李译之出谢使一行。必有密启而时未得见。敕使渡江后。似可知之是白齐。得闻谢行先出。则虑有恐动之说故。使之落后云云为白齐。且闻在北京时。有七敕并出之说。且有率甲军三百。分驻湾上之议。而七敕中一员既减之后。则分驻之说乃寝。到凤城初。有甲军调发之状。而此亦还止是如。臣军官乘隙密闻中使之言而来传所闻如此。敢为驰启为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
[湾上秘启(庚寅迎六敕于湾上时)]
谢恩使密启果为付来。而常加搜括故。李译卜鞍之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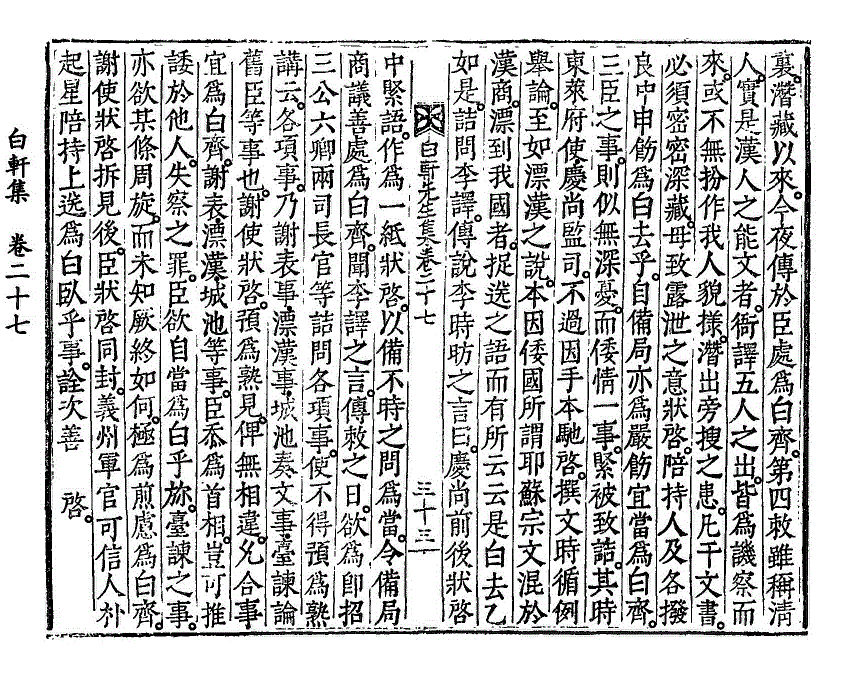 里。潜藏以来。今夜传于臣处为白齐。第四敕虽称清人。实是汉人之能文者。衙译五人之出。皆为讥察而来。或不无扮作我人貌样。潜出旁搜之患。凡干文书。必须密密深藏。毋致露泄之意状启。陪持人及各拨良中申饬为白去乎。自备局亦为严饬宜当为白齐。三臣之事。则似无深忧。而倭情一事。紧被致诘。其时东莱府使庆尚监司。不过因手本驰启。撰文时循例举论。至如漂汉之说。本因倭国所谓耶苏宗文混于汉商。漂到我国者。捉送之语而有所云云是白去乙如是。诘问李译。传说李时昉之言曰。庆尚前后状启中紧语。作为一纸状启。以备不时之问为当。令备局商议善处为白齐。闻李译之言。传敕之日。欲为即招三公六卿两司长官等诘问各项事。使不得预为熟讲云。各项事。乃谢表事,漂汉事,城池奏文事,台谏论旧臣等事也。谢使状启。预为熟见。俾无相违。允合事宜为白齐。谢表,漂汉,城池等事。臣忝为首相。岂可推诿于他人。失察之罪。臣欲自当为白乎旀。台谏之事。亦欲某条周旋。而未知厥终如何。极为煎虑为白齐。谢使状启拆见后。臣状启同封。义州军官可信人朴起星陪持上送为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
里。潜藏以来。今夜传于臣处为白齐。第四敕虽称清人。实是汉人之能文者。衙译五人之出。皆为讥察而来。或不无扮作我人貌样。潜出旁搜之患。凡干文书。必须密密深藏。毋致露泄之意状启。陪持人及各拨良中申饬为白去乎。自备局亦为严饬宜当为白齐。三臣之事。则似无深忧。而倭情一事。紧被致诘。其时东莱府使庆尚监司。不过因手本驰启。撰文时循例举论。至如漂汉之说。本因倭国所谓耶苏宗文混于汉商。漂到我国者。捉送之语而有所云云是白去乙如是。诘问李译。传说李时昉之言曰。庆尚前后状启中紧语。作为一纸状启。以备不时之问为当。令备局商议善处为白齐。闻李译之言。传敕之日。欲为即招三公六卿两司长官等诘问各项事。使不得预为熟讲云。各项事。乃谢表事,漂汉事,城池奏文事,台谏论旧臣等事也。谢使状启。预为熟见。俾无相违。允合事宜为白齐。谢表,漂汉,城池等事。臣忝为首相。岂可推诿于他人。失察之罪。臣欲自当为白乎旀。台谏之事。亦欲某条周旋。而未知厥终如何。极为煎虑为白齐。谢使状启拆见后。臣状启同封。义州军官可信人朴起星陪持上送为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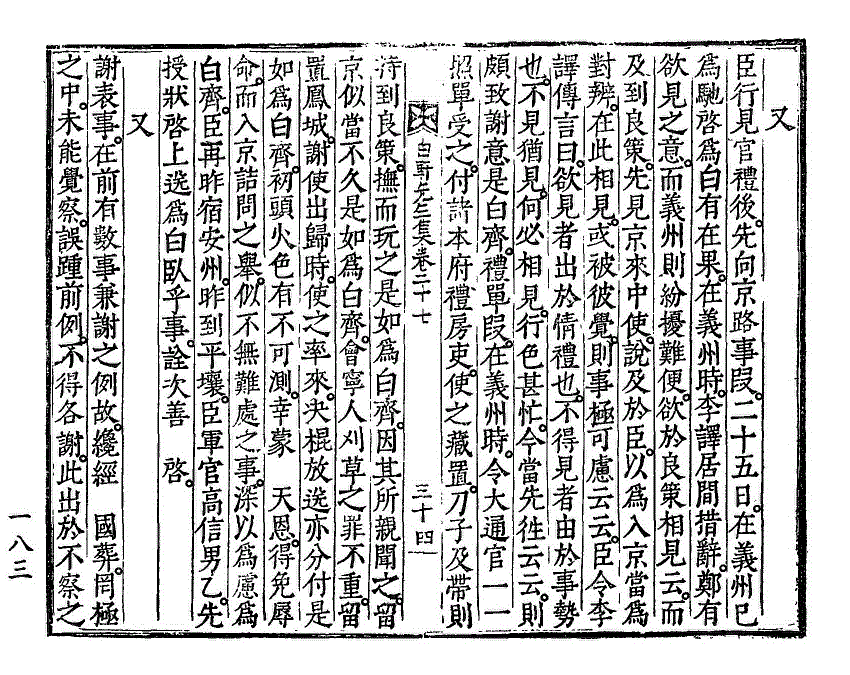 [湾上秘启(庚寅迎六敕于湾上时)]
[湾上秘启(庚寅迎六敕于湾上时)]臣行见官礼后。先向京路事段。二十五日。在义州已为驰启为白有在果。在义州时。李译居间措辞。郑有欲见之意。而义州则纷扰难便。欲于良策相见云。而及到良策。先见京来中使。说及于臣。以为入京当为对辨。在此相见。或被彼觉。则事极可虑云云。臣令李译传言曰。欲见者出于情礼也。不得见者由于事势也。不见犹见。何必相见。行色甚忙。今当先往云云。则颇致谢意是白齐。礼单段。在义州时。令大通官一一照单受之。付诸本府礼房吏。使之藏置。刀子及带则持到良策。抚而玩之是如为白齐。因其所亲闻之。留京似当不久是如为白齐。会宁人刈草之罪不重。留置凤城。谢使出归时。使之率来。决棍放送亦分付是如为白齐。初头火色有不可测。幸蒙 天恩。得免辱命。而入京诘问之举。似不无难处之事。深以为虑为白齐。臣再昨宿安州。昨到平壤。臣军官高信男乙。先授状启上送为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
[湾上秘启(庚寅迎六敕于湾上时)]
谢表事。在前有数事兼谢之例故。才经 国葬。罔极之中。未能觉察。误踵前例。不得各谢。此出于不察之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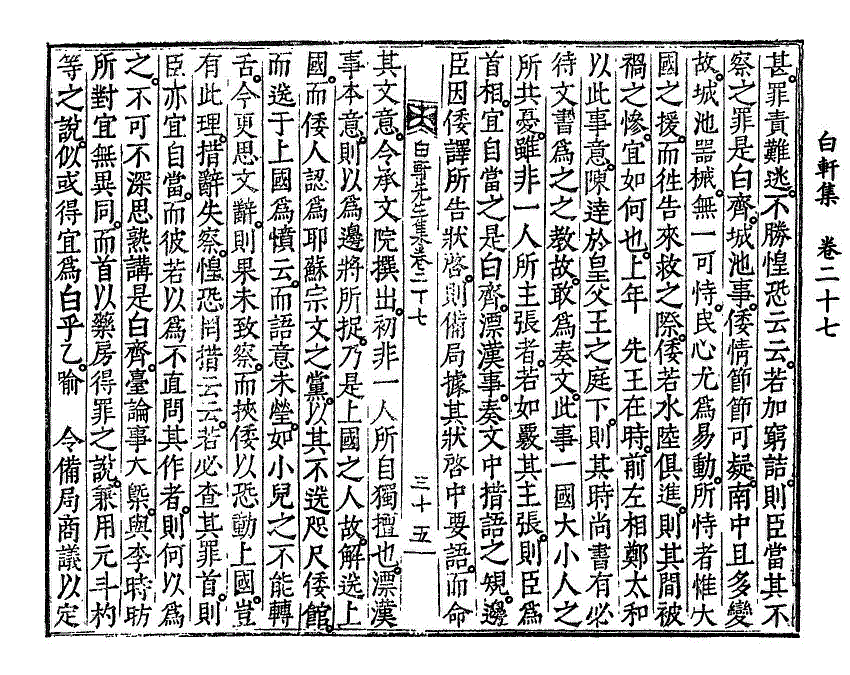 甚。罪责难逃。不胜惶恐云云。若加穷诘。则臣当其不察之罪是白齐。城池事。倭情节节可疑。南中且多变故。城池器械。无一可恃。民心尤为易动。所恃者惟大国之援。而往告来救之际。倭若水陆俱进。则其间被祸之惨。宜如何也。上年 先王在时。前左相郑太和以此事意。陈达于皇父王之庭下。则其时尚书有必待文书为之之教故。敢为奏文。此事一国大小人之所共忧。虽非一人所主张者。若如覈其主张。则臣为首相。宜自当之是白齐。漂汉事。奏文中措语之规。边臣因倭译所告状启。则备局据其状启中要语。而命其文意。令承文院撰出。初非一人所自独擅也。漂汉事本意。则以为边将所捉。乃是上国之人故。解送上国。而倭人认为耶苏宗文之党。以其不送咫尺倭馆。而送于上国为愤云。而语意未莹。如小儿之不能转舌。今更思文辞。则果未致察。而挟倭以恐动上国。岂有此理。措辞失察。惶恐罔措云云。若必查其罪首。则臣亦宜自当。而彼若以为不直问其作者。则何以为之。不可不深思熟讲是白齐。台论事大槩。与李时昉所对宜无异同。而首以药房得罪之说。兼用元斗杓等之说。似或得宜为白乎乙。喻 令备局商议以定
甚。罪责难逃。不胜惶恐云云。若加穷诘。则臣当其不察之罪是白齐。城池事。倭情节节可疑。南中且多变故。城池器械。无一可恃。民心尤为易动。所恃者惟大国之援。而往告来救之际。倭若水陆俱进。则其间被祸之惨。宜如何也。上年 先王在时。前左相郑太和以此事意。陈达于皇父王之庭下。则其时尚书有必待文书为之之教故。敢为奏文。此事一国大小人之所共忧。虽非一人所主张者。若如覈其主张。则臣为首相。宜自当之是白齐。漂汉事。奏文中措语之规。边臣因倭译所告状启。则备局据其状启中要语。而命其文意。令承文院撰出。初非一人所自独擅也。漂汉事本意。则以为边将所捉。乃是上国之人故。解送上国。而倭人认为耶苏宗文之党。以其不送咫尺倭馆。而送于上国为愤云。而语意未莹。如小儿之不能转舌。今更思文辞。则果未致察。而挟倭以恐动上国。岂有此理。措辞失察。惶恐罔措云云。若必查其罪首。则臣亦宜自当。而彼若以为不直问其作者。则何以为之。不可不深思熟讲是白齐。台论事大槩。与李时昉所对宜无异同。而首以药房得罪之说。兼用元斗杓等之说。似或得宜为白乎乙。喻 令备局商议以定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文稿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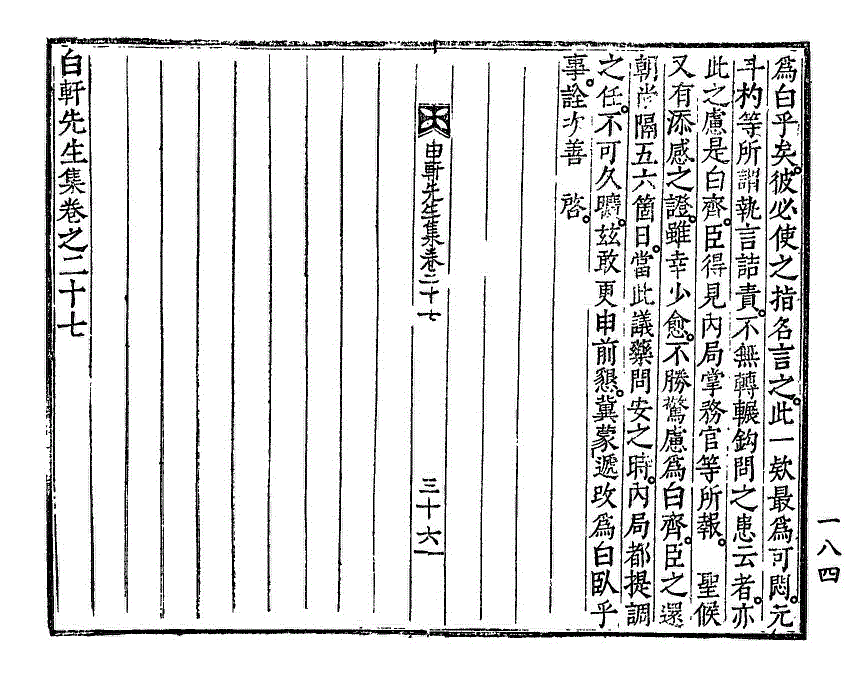 为白乎矣。彼必使之指名言之。此一款最为可闷。元斗杓等所谓执言诘责。不无转辗钩问之患云者。亦此之虑是白齐。臣得见内局掌务官等所报。 圣候又有添感之證。虽幸少愈。不胜惊虑为白齐。臣之还朝尚隔五六个日。当此议药问安之时。内局都提调之任。不可久旷。玆敢更申前恳。冀蒙递改为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
为白乎矣。彼必使之指名言之。此一款最为可闷。元斗杓等所谓执言诘责。不无转辗钩问之患云者。亦此之虑是白齐。臣得见内局掌务官等所报。 圣候又有添感之證。虽幸少愈。不胜惊虑为白齐。臣之还朝尚隔五六个日。当此议药问安之时。内局都提调之任。不可久旷。玆敢更申前恳。冀蒙递改为白卧乎事。诠次善 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