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x 页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疏劄
疏劄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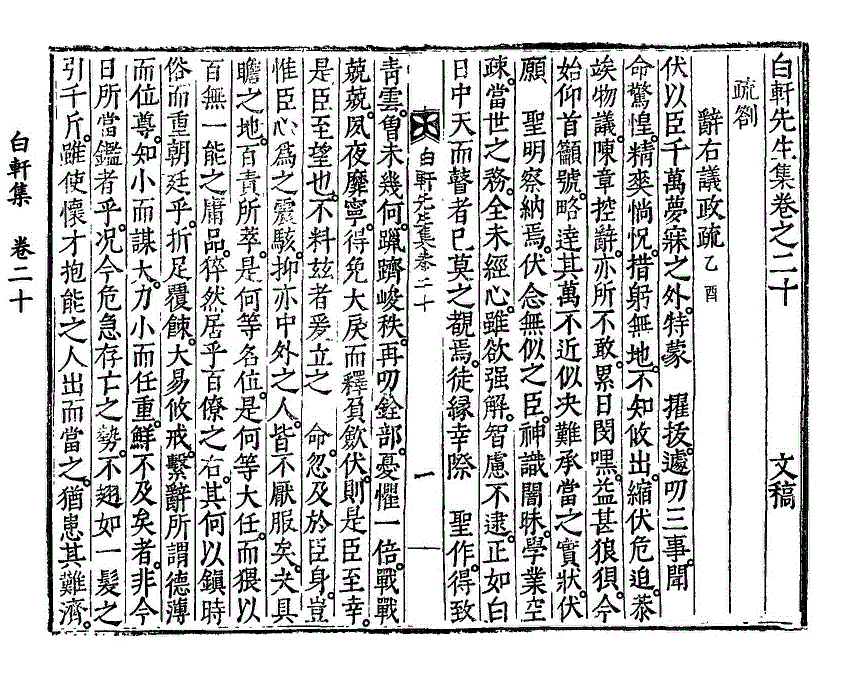 辞右议政疏(乙酉)
辞右议政疏(乙酉)伏以臣千万梦寐之外。特蒙 擢拔。遽叨三事。闻 命惊惶。精爽惝恍。措躬无地。不知攸出。缩伏危迫。恭俟物议。陈章控辞。亦所不敢。累日闵嘿。益甚狼狈。今始仰首吁号。略达其万不近似决难承当之实状。伏愿 圣明察纳焉。伏念无似之臣。神识闇昧。学业空疏。当世之务。全未经心。虽欲强解。智虑不逮。正如白日中天而瞽者已莫之睹焉。徒缘幸际 圣作。得致青云。曾未几何。躐跻峻秩。再叨铨部。忧惧一倍。战战兢兢。夙夜靡宁。得免大戾而释负敛伏。则是臣至幸。是臣至望也。不料玆者爰立之 命。忽及于臣身。岂惟臣心为之震骇。抑亦中外之人。皆不厌服矣。夫具瞻之地。百责所萃。是何等名位。是何等大任。而猥以百无一能之庸品。猝然居乎百僚之右。其何以镇时俗而重朝廷乎。折足覆餗。大易攸戒。系辞所谓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者。非今日所当鉴者乎。况今危急存亡之势。不翅如一发之引千斤。虽使怀才抱能之人出而当之。犹患其难济。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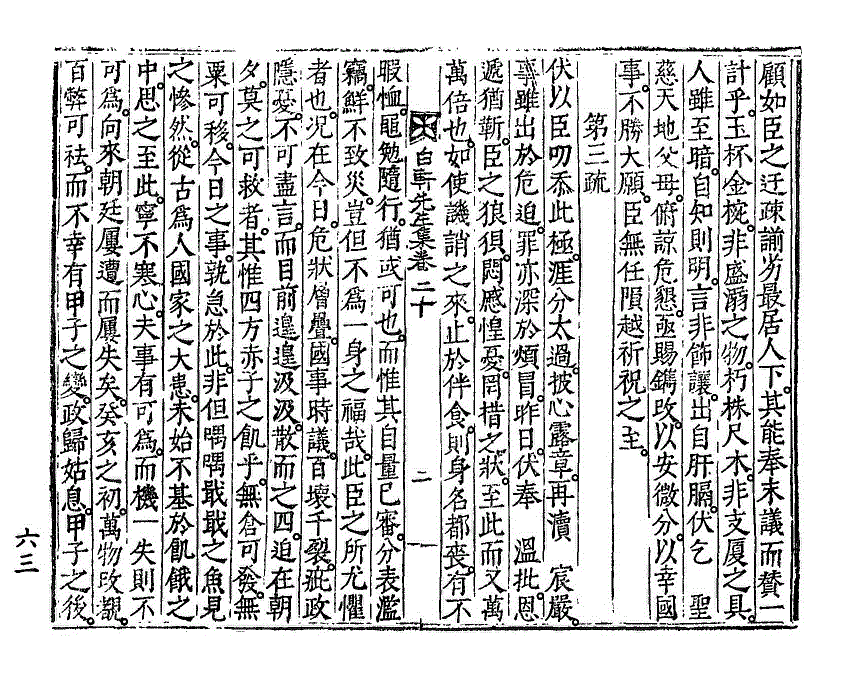 顾如臣之迂疏谫劣最居人下。其能奉末议而赞一计乎。玉杯金碗。非盛溺之物。朽株尺木。非支厦之具。人虽至暗。自知则明。言非饰让。出自肝膈。伏乞 圣慈天地父母。俯谅危恳。亟赐镌改。以安微分。以幸国事。不胜大愿。臣无任陨越祈祝之至。
顾如臣之迂疏谫劣最居人下。其能奉末议而赞一计乎。玉杯金碗。非盛溺之物。朽株尺木。非支厦之具。人虽至暗。自知则明。言非饰让。出自肝膈。伏乞 圣慈天地父母。俯谅危恳。亟赐镌改。以安微分。以幸国事。不胜大愿。臣无任陨越祈祝之至。辞右议政疏(乙酉)[第三疏]
伏以臣叨忝此极。涯分太过。披心露章。再渎 宸严。事虽出于危迫。罪亦深于烦冒。昨日。伏奉 温批。恩递犹靳。臣之狼狈。闷戚惶忧。罔措之状。至此而又万万倍也。如使讥诮之来。止于伴食。则身名都丧。有不暇恤。黾勉随行。犹或可也。而惟其自量已审。分表滥窃。鲜不致灾。岂但不为一身之福哉。此臣之所尤惧者也。况在今日。危状层叠。国事时议。百坏千裂。疵政隐忧。不可尽言。而目前遑遑汲汲。散而之四。迫在朝夕。莫之可救者。其惟四方赤子之饥乎。无仓可发。无粟可移。今日之事。孰急于此。非但喁喁戢戢之鱼见之惨然。从古为人国家之大患。未始不基于饥饿之中。思之至此。宁不寒心。夫事有可为。而机一失则不可为。向来朝廷屡遭而屡失矣。癸亥之初。万物改睹。百弊可祛。而不幸有甲子之变。政归姑息。甲子之后。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4H 页
 有丁卯之变。丁卯之后。有丙子之变。夫丧邦恒于变。兴邦恒于变。因变而施措得宜。则国罔不兴。施措失宜。则国日以危。终至于亡矣。噫变至于丙丁而惨矣。施措亦可谓失宜矣。而然而尚保延延之一脉者。以 圣明在上焉耳。究厥失宜之原。则何尝不在于一私字害之也。所谓私者。非必纵欲之谓也。凡见事之可行而不肯行者。皆是私也。试以一事言之。有司之臣。各私其司。不思共济国事。京外之官。莫不皆然。至于是非之际。亦各自执其偏。纷纭舛错如是。而尚复望其一事之有成乎。法之不能行。私也。泽之不能究。私也。才贤之不能进。私也。目今大命近止。其亦殆哉。而抑固结人心。迓续景命。亦惟在于此时。若失此机。更无可为之势。伏见近来自 上裁处之事。进供方物。尽行减免。凡系保民之政。一一采施。其轸念图存之意。至矣尽矣。岂天之降灾。将以启 殿下之圣而兴殿下之邦耶。何其幸也。在下者苟能上体圣意。下念时诎。各祛其私。各蠲其役。各捐其储。夙宵一念。无不在于恤民。尺木斗米。无不归于救民。如饥者之就食渴者之赴泉焉。则国事庶可济矣。而谁能使之办此。虽然。臣之所谓救民者。大段用力之谓也。非寻常
有丁卯之变。丁卯之后。有丙子之变。夫丧邦恒于变。兴邦恒于变。因变而施措得宜。则国罔不兴。施措失宜。则国日以危。终至于亡矣。噫变至于丙丁而惨矣。施措亦可谓失宜矣。而然而尚保延延之一脉者。以 圣明在上焉耳。究厥失宜之原。则何尝不在于一私字害之也。所谓私者。非必纵欲之谓也。凡见事之可行而不肯行者。皆是私也。试以一事言之。有司之臣。各私其司。不思共济国事。京外之官。莫不皆然。至于是非之际。亦各自执其偏。纷纭舛错如是。而尚复望其一事之有成乎。法之不能行。私也。泽之不能究。私也。才贤之不能进。私也。目今大命近止。其亦殆哉。而抑固结人心。迓续景命。亦惟在于此时。若失此机。更无可为之势。伏见近来自 上裁处之事。进供方物。尽行减免。凡系保民之政。一一采施。其轸念图存之意。至矣尽矣。岂天之降灾。将以启 殿下之圣而兴殿下之邦耶。何其幸也。在下者苟能上体圣意。下念时诎。各祛其私。各蠲其役。各捐其储。夙宵一念。无不在于恤民。尺木斗米。无不归于救民。如饥者之就食渴者之赴泉焉。则国事庶可济矣。而谁能使之办此。虽然。臣之所谓救民者。大段用力之谓也。非寻常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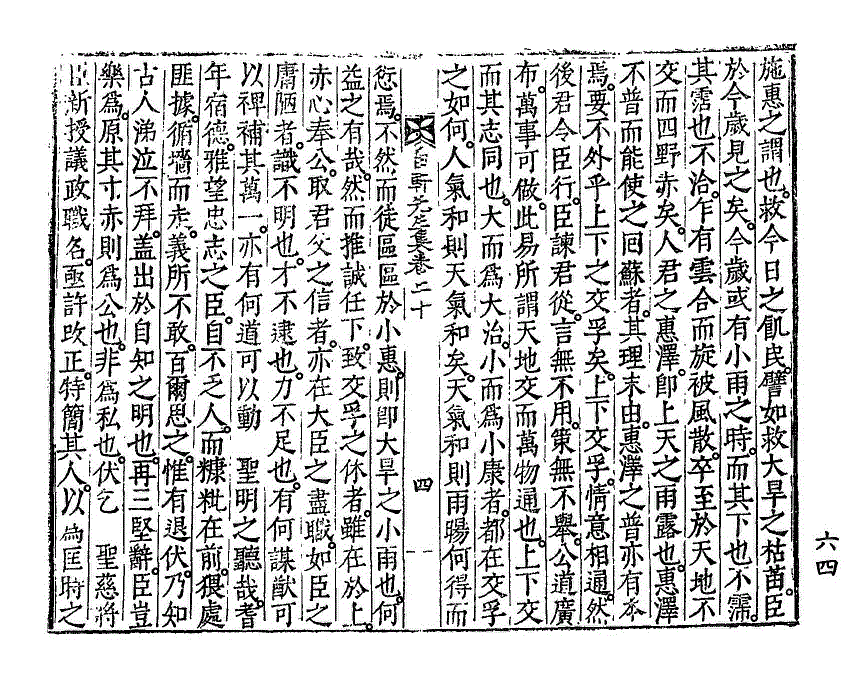 施惠之谓也。救今日之饥民。譬如救大旱之枯苗。臣于今岁见之矣。今岁或有小雨之时。而其下也不霈。其沾也不洽。乍有云合而旋被风散。卒至于天地不交而四野赤矣。人君之惠泽。即上天之雨露也。惠泽不普而能使之回苏者。其理末由。惠泽之普亦有本焉。要不外乎上下之交孚矣。上下交孚。情意相通。然后君令臣行。臣谏君从。言无不用。策无不举。公道广布。万事可做。此易所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大而为大治。小而为小康者。都在交孚之如何。人气和则天气和矣。天气和则雨旸何得而愆焉。不然而徒区区于小惠。则即大旱之小雨也。何益之有哉。然而推诚任下。致交孚之休者。虽在于上。赤心奉公。取君父之信者。亦在大臣之尽职。如臣之庸陋者。识不明也。才不逮也。力不足也。有何谋猷可以裨补其万一。亦有何道可以动 圣明之听哉。耆年宿德。雅望忠志之臣。自不乏人。而糠秕在前。猥处匪据。循墙而走。义所不敢。百尔思之。惟有退伏。乃知古人涕泣不拜。盖出于自知之明也。再三坚辞。臣岂乐为。原其寸赤则为公也。非为私也。伏乞 圣慈将臣新授议政职名。亟许改正。特简其人。以为匡时之
施惠之谓也。救今日之饥民。譬如救大旱之枯苗。臣于今岁见之矣。今岁或有小雨之时。而其下也不霈。其沾也不洽。乍有云合而旋被风散。卒至于天地不交而四野赤矣。人君之惠泽。即上天之雨露也。惠泽不普而能使之回苏者。其理末由。惠泽之普亦有本焉。要不外乎上下之交孚矣。上下交孚。情意相通。然后君令臣行。臣谏君从。言无不用。策无不举。公道广布。万事可做。此易所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大而为大治。小而为小康者。都在交孚之如何。人气和则天气和矣。天气和则雨旸何得而愆焉。不然而徒区区于小惠。则即大旱之小雨也。何益之有哉。然而推诚任下。致交孚之休者。虽在于上。赤心奉公。取君父之信者。亦在大臣之尽职。如臣之庸陋者。识不明也。才不逮也。力不足也。有何谋猷可以裨补其万一。亦有何道可以动 圣明之听哉。耆年宿德。雅望忠志之臣。自不乏人。而糠秕在前。猥处匪据。循墙而走。义所不敢。百尔思之。惟有退伏。乃知古人涕泣不拜。盖出于自知之明也。再三坚辞。臣岂乐为。原其寸赤则为公也。非为私也。伏乞 圣慈将臣新授议政职名。亟许改正。特简其人。以为匡时之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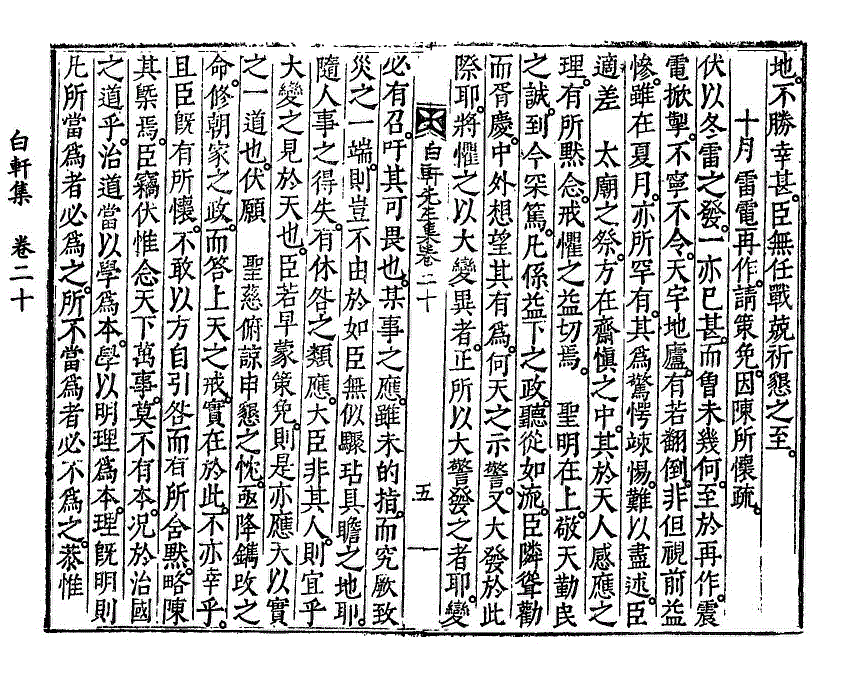 地。不胜幸甚。臣无任战兢祈恳之至。
地。不胜幸甚。臣无任战兢祈恳之至。十月雷电再作。请策免。因陈所怀疏。
伏以冬雷之发。一亦已甚。而曾未几何。至于再作。震电掀掣。不宁不令。天宇地庐。有若翻倒。非但视前益惨。虽在夏月。亦所罕有。其为惊愕竦惕。难以尽述。臣适差 太庙之祭。方在斋慎之中。其于天人感应之理。有所默念。戒惧之益切焉。 圣明在上。敬天勤民之诚。到今深笃。凡系益下之政。听从如流。臣邻耸劝而胥庆。中外想望其有为。何天之示警。又大发于此际耶。将惧之以大变异者。正所以大警发之者耶。变必有召。吁其可畏也。某事之应。虽未的指。而究厥致灾之一端。则岂不由于如臣无似骤玷具瞻之地耶。随人事之得失。有休咎之类应。大臣非其人。则宜乎大变之见于天也。臣若早蒙策免。则是亦应天以实之一道也。伏愿 圣慈俯谅申恳之忱。亟降镌改之命。修朝家之政。而答上天之戒。实在于此。不亦幸乎。且臣既有所怀。不敢以方自引咎而有所含默。略陈其槩焉。臣窃伏惟念天下万事。莫不有本。况于治国之道乎。治道当以学为本。学以明理为本。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者必为之。所不当为者必不为之。恭惟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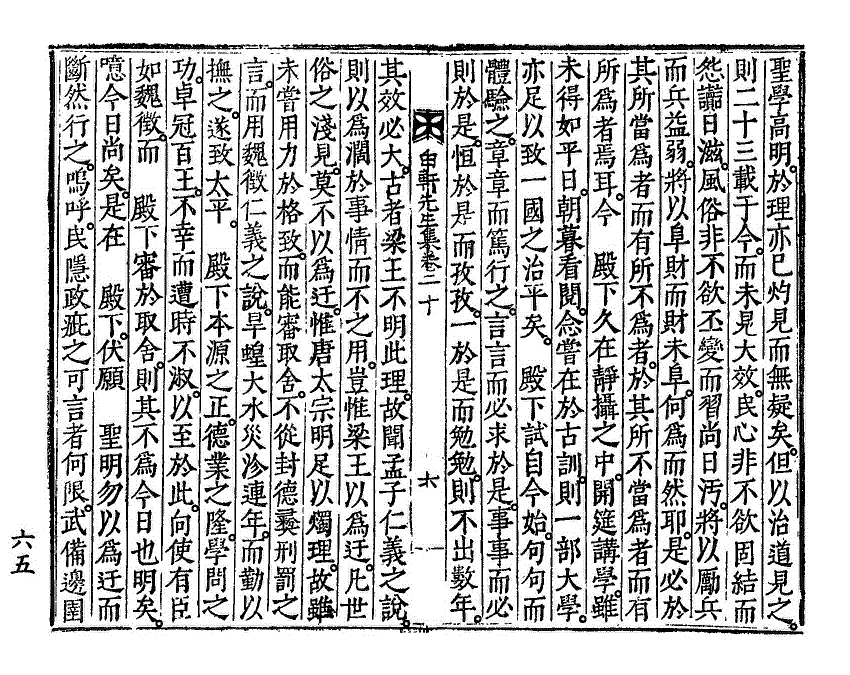 圣学高明。于理亦已灼见而无疑矣。但以治道见之。则二十三载于今。而未见大效。民心非不欲固结而怨讟日滋。风俗非不欲丕变而习尚日污。将以励兵而兵益弱。将以阜财而财未阜。何为而然耶。是必于其所当为者而有所不为者。于其所不当为者而有所为者焉耳。今 殿下久在静摄之中。开筵讲学。虽未得如平日。朝暮看阅。念尝在于古训。则一部大学。亦足以致一国之治平矣。 殿下试自今始。句句而体验之。章章而笃行之。言言而必求于是。事事而必则于是。恒于是而孜孜。一于是而勉勉。则不出数年。其效必大。古者梁王不明此理。故闻孟子仁义之说。则以为阔于事情而不之用。岂惟梁王以为迂。凡世俗之浅见。莫不以为迂。惟唐太宗明足以烛理。故虽未尝用力于格致。而能审取舍。不从封德彝刑罚之言。而用魏徵仁义之说。旱蝗大水灾沴连年。而勤以抚之。遂致太平。 殿下本源之正。德业之隆。学问之功。卓冠百王。不幸而遭时不淑。以至于此。向使有臣如魏徵。而 殿下审于取舍。则其不为今日也明矣。噫今日尚矣。是在 殿下。伏愿 圣明勿以为迂而断然行之。呜呼。民隐政疵之可言者何限。武备边圉
圣学高明。于理亦已灼见而无疑矣。但以治道见之。则二十三载于今。而未见大效。民心非不欲固结而怨讟日滋。风俗非不欲丕变而习尚日污。将以励兵而兵益弱。将以阜财而财未阜。何为而然耶。是必于其所当为者而有所不为者。于其所不当为者而有所为者焉耳。今 殿下久在静摄之中。开筵讲学。虽未得如平日。朝暮看阅。念尝在于古训。则一部大学。亦足以致一国之治平矣。 殿下试自今始。句句而体验之。章章而笃行之。言言而必求于是。事事而必则于是。恒于是而孜孜。一于是而勉勉。则不出数年。其效必大。古者梁王不明此理。故闻孟子仁义之说。则以为阔于事情而不之用。岂惟梁王以为迂。凡世俗之浅见。莫不以为迂。惟唐太宗明足以烛理。故虽未尝用力于格致。而能审取舍。不从封德彝刑罚之言。而用魏徵仁义之说。旱蝗大水灾沴连年。而勤以抚之。遂致太平。 殿下本源之正。德业之隆。学问之功。卓冠百王。不幸而遭时不淑。以至于此。向使有臣如魏徵。而 殿下审于取舍。则其不为今日也明矣。噫今日尚矣。是在 殿下。伏愿 圣明勿以为迂而断然行之。呜呼。民隐政疵之可言者何限。武备边圉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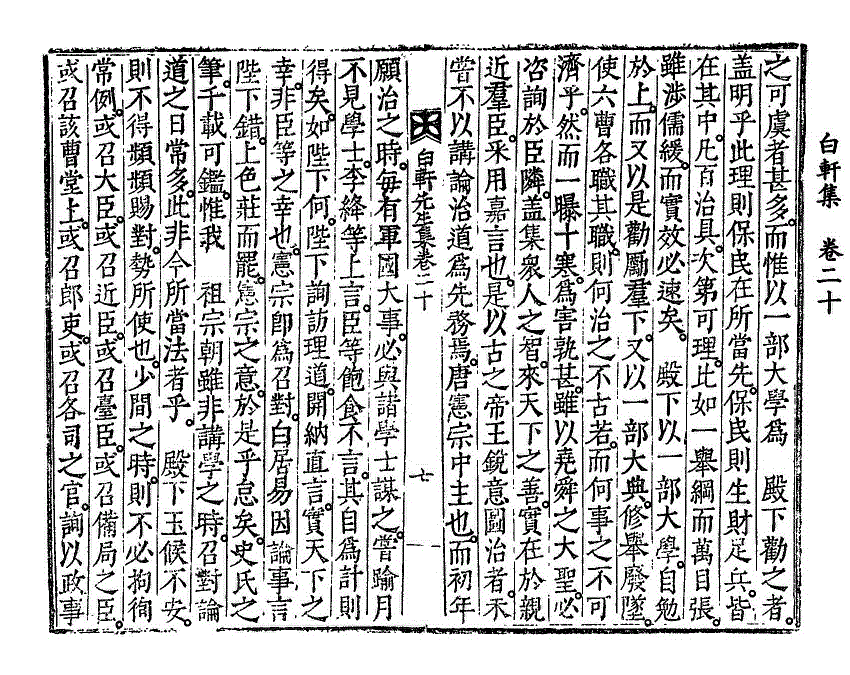 之可虞者甚多。而惟以一部大学为 殿下劝之者。盖明乎此理则保民在所当先。保民则生财足兵。皆在其中。凡百治具。次第可理。比如一举纲而万目张。虽涉儒缓。而实效必速矣。 殿下以一部大学。自勉于上。而又以是劝励群下。又以一部大典。修举废坠。使六曹各职其职。则何治之不古若。而何事之不可济乎。然而一曝十寒。为害孰甚。虽以尧舜之大圣。必咨询于臣邻。盖集众人之智。来天下之善。实在于亲近群臣。采用嘉言也。是以古之帝王锐意图治者。禾尝不以讲论治道为先务焉。唐宪宗中主也。而初年愿治之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踰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宪宗即为召对。白居易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宪宗之意。于是乎怠矣。史氏之笔。千载可鉴。惟我 祖宗朝虽非讲学之时。召对论道之日常多。此非今所当法者乎。 殿下玉候不安。则不得频频赐对。势所使也。少间之时。则不必拘徇常例。或召大臣。或召近臣。或召台臣。或召备局之臣。或召该曹堂上。或召郎吏。或召各司之官。询以政事
之可虞者甚多。而惟以一部大学为 殿下劝之者。盖明乎此理则保民在所当先。保民则生财足兵。皆在其中。凡百治具。次第可理。比如一举纲而万目张。虽涉儒缓。而实效必速矣。 殿下以一部大学。自勉于上。而又以是劝励群下。又以一部大典。修举废坠。使六曹各职其职。则何治之不古若。而何事之不可济乎。然而一曝十寒。为害孰甚。虽以尧舜之大圣。必咨询于臣邻。盖集众人之智。来天下之善。实在于亲近群臣。采用嘉言也。是以古之帝王锐意图治者。禾尝不以讲论治道为先务焉。唐宪宗中主也。而初年愿治之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踰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宪宗即为召对。白居易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宪宗之意。于是乎怠矣。史氏之笔。千载可鉴。惟我 祖宗朝虽非讲学之时。召对论道之日常多。此非今所当法者乎。 殿下玉候不安。则不得频频赐对。势所使也。少间之时。则不必拘徇常例。或召大臣。或召近臣。或召台臣。或召备局之臣。或召该曹堂上。或召郎吏。或召各司之官。询以政事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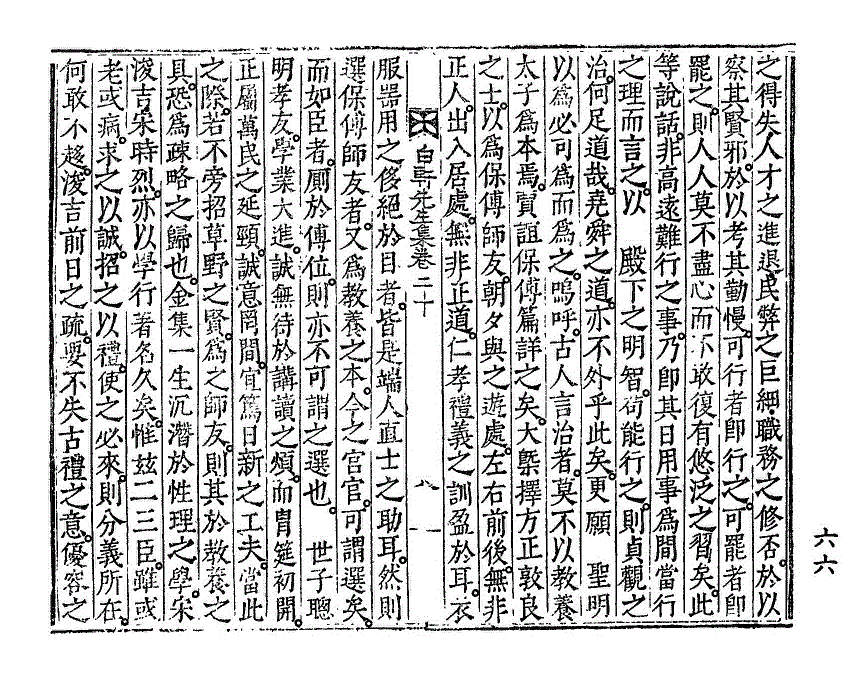 之得失,人才之进退,民弊之巨细,职务之修否。于以察其贤邪。于以考其勤慢。可行者即行之。可罢者即罢之。则人人莫不尽心而不敢复有悠泛之习矣。此等说话。非高远难行之事。乃即其日用事为间当行之理而言之。以 殿下之明智。苟能行之。则贞观之治。何足道哉。尧舜之道。亦不外乎此矣。更愿 圣明以为必可为而为之。呜呼。古人言治者。莫不以教养太子为本焉。贾谊保傅篇详之矣。大槩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居处。无非正道。仁孝礼义之训盈于耳。衣服器用之侈绝于目者。皆是端人直士之助耳。然则选保傅师友者。又为教养之本。今之宫官。可谓选矣。而如臣者。厕于傅位。则亦不可谓之选也。 世子聪明孝友。学业大进。诚无待于讲读之烦。而胄筵初开。正属万民之延颈。诚意罔间。宜笃日新之工夫。当此之际。若不旁招草野之贤。为之师友。则其于教养之具。恐为疏略之归也。金集一生沈潜于性理之学。宋浚吉,宋时烈。亦以学行著名久矣。惟玆二三臣。虽或老或病。求之以诚。招之以礼。使之必来。则分义所在。何敢不趋。浚吉前日之疏。要不失古礼之意。优容之
之得失,人才之进退,民弊之巨细,职务之修否。于以察其贤邪。于以考其勤慢。可行者即行之。可罢者即罢之。则人人莫不尽心而不敢复有悠泛之习矣。此等说话。非高远难行之事。乃即其日用事为间当行之理而言之。以 殿下之明智。苟能行之。则贞观之治。何足道哉。尧舜之道。亦不外乎此矣。更愿 圣明以为必可为而为之。呜呼。古人言治者。莫不以教养太子为本焉。贾谊保傅篇详之矣。大槩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居处。无非正道。仁孝礼义之训盈于耳。衣服器用之侈绝于目者。皆是端人直士之助耳。然则选保傅师友者。又为教养之本。今之宫官。可谓选矣。而如臣者。厕于傅位。则亦不可谓之选也。 世子聪明孝友。学业大进。诚无待于讲读之烦。而胄筵初开。正属万民之延颈。诚意罔间。宜笃日新之工夫。当此之际。若不旁招草野之贤。为之师友。则其于教养之具。恐为疏略之归也。金集一生沈潜于性理之学。宋浚吉,宋时烈。亦以学行著名久矣。惟玆二三臣。虽或老或病。求之以诚。招之以礼。使之必来。则分义所在。何敢不趋。浚吉前日之疏。要不失古礼之意。优容之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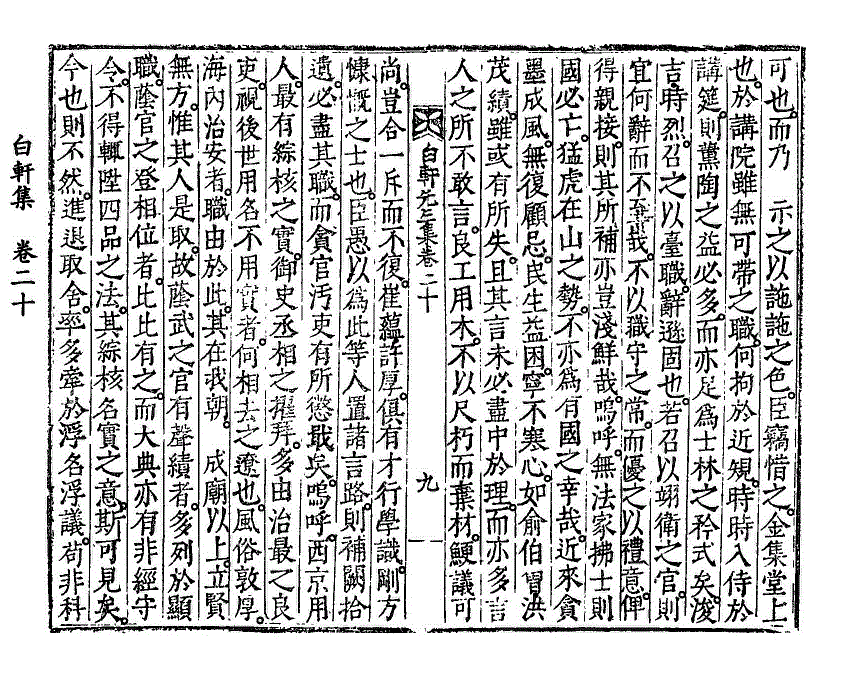 可也。而乃 示之以訑訑之色。臣窃惜之。金集堂上也。于讲院虽无可带之职。何拘于近规。时时入侍于讲筵。则薰陶之益必多。而亦足为士林之矜式矣。浚吉,时烈。召之以台职。辞逊固也。若召以翊卫之官。则宜何辞而不至哉。不以职守之常。而优之以礼意。俾得亲接。则其所补亦岂浅鲜哉。呜呼。无法家拂士则国必亡。猛虎在山之势。不亦为有国之幸哉。近来贪墨成风。无复顾忌。民生益困。宁不寒心。如俞伯曾,洪茂绩。虽或有所失。且其言未必尽中于理。而亦多言人之所不敢言。良工用木。不以尺朽而弃材。鲠议可尚。岂合一斥而不复。崔蕴,许厚。俱有才行学识。刚方慷慨之士也。臣愚以为此等人置诸言路。则补阙拾遗。必尽其职。而贪官污吏有所惩戢矣。呜呼。西京用人。最有综核之实。御史丞相之擢拜。多由治最之良吏。视后世用名不用实者。何相去之辽也。风俗敦厚。海内治安者。职由于此。其在我朝。 成庙以上。立贤无方。惟其人是取。故荫武之官有声绩者。多列于显职。荫官之登相位者。比比有之。而大典亦有非经守令。不得辄升四品之法。其综核名实之意。斯可见矣。今也则不然。进退取舍。率多牵于浮名浮议。苟非科
可也。而乃 示之以訑訑之色。臣窃惜之。金集堂上也。于讲院虽无可带之职。何拘于近规。时时入侍于讲筵。则薰陶之益必多。而亦足为士林之矜式矣。浚吉,时烈。召之以台职。辞逊固也。若召以翊卫之官。则宜何辞而不至哉。不以职守之常。而优之以礼意。俾得亲接。则其所补亦岂浅鲜哉。呜呼。无法家拂士则国必亡。猛虎在山之势。不亦为有国之幸哉。近来贪墨成风。无复顾忌。民生益困。宁不寒心。如俞伯曾,洪茂绩。虽或有所失。且其言未必尽中于理。而亦多言人之所不敢言。良工用木。不以尺朽而弃材。鲠议可尚。岂合一斥而不复。崔蕴,许厚。俱有才行学识。刚方慷慨之士也。臣愚以为此等人置诸言路。则补阙拾遗。必尽其职。而贪官污吏有所惩戢矣。呜呼。西京用人。最有综核之实。御史丞相之擢拜。多由治最之良吏。视后世用名不用实者。何相去之辽也。风俗敦厚。海内治安者。职由于此。其在我朝。 成庙以上。立贤无方。惟其人是取。故荫武之官有声绩者。多列于显职。荫官之登相位者。比比有之。而大典亦有非经守令。不得辄升四品之法。其综核名实之意。斯可见矣。今也则不然。进退取舍。率多牵于浮名浮议。苟非科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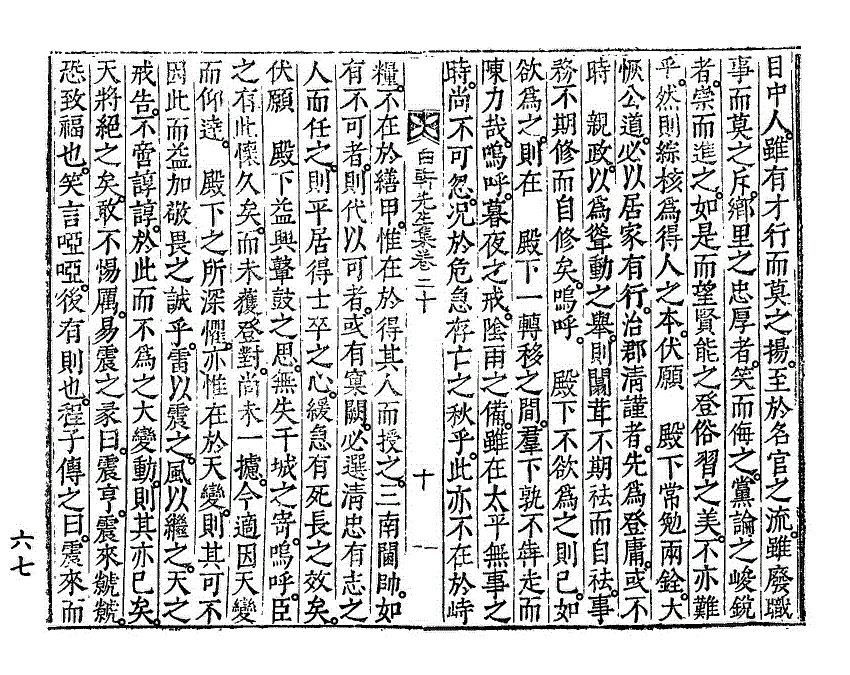 目中人。虽有才行而莫之扬。至于名官之流。虽废职事而莫之斥。乡里之忠厚者。笑而侮之。党论之峻锐者。崇而进之。如是而望贤能之登俗习之美。不亦难乎。然则综核为得人之本。伏愿 殿下常勉两铨。大恢公道。必以居家有行。治郡清谨者。先为登庸。或不时 亲政。以为耸动之举。则阘茸不期祛而自祛。事务不期修而自修矣。呜呼。 殿下不欲为之则已。如欲为之。则在 殿下一转移之间。群下孰不奔走而陈力哉。呜呼。暮夜之戒。阴雨之备。虽在太平无事之时。尚不可忽。况于危急存亡之秋乎。此亦不在于峙粮。不在于缮甲。惟在于得其人而授之。三南阃帅。如有不可者。则代以可者。或有窠阙。必选清忠有志之人而任之。则平居得士卒之心。缓急有死长之效矣。伏愿 殿下益兴鼙鼓之思。无失干城之寄。呜呼。臣之有此怀久矣。而未获登对。尚未一摅。今适因天变而仰达。 殿下之所深惧。亦惟在于天变。则其可不因此而益加敬畏之诚乎。雷以震之。风以继之。天之戒告。不啻谆谆。于此而不为之大变动。则其亦已矣。天将绝之矣。敢不惕厉。易震之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程子传之曰。震来而
目中人。虽有才行而莫之扬。至于名官之流。虽废职事而莫之斥。乡里之忠厚者。笑而侮之。党论之峻锐者。崇而进之。如是而望贤能之登俗习之美。不亦难乎。然则综核为得人之本。伏愿 殿下常勉两铨。大恢公道。必以居家有行。治郡清谨者。先为登庸。或不时 亲政。以为耸动之举。则阘茸不期祛而自祛。事务不期修而自修矣。呜呼。 殿下不欲为之则已。如欲为之。则在 殿下一转移之间。群下孰不奔走而陈力哉。呜呼。暮夜之戒。阴雨之备。虽在太平无事之时。尚不可忽。况于危急存亡之秋乎。此亦不在于峙粮。不在于缮甲。惟在于得其人而授之。三南阃帅。如有不可者。则代以可者。或有窠阙。必选清忠有志之人而任之。则平居得士卒之心。缓急有死长之效矣。伏愿 殿下益兴鼙鼓之思。无失干城之寄。呜呼。臣之有此怀久矣。而未获登对。尚未一摅。今适因天变而仰达。 殿下之所深惧。亦惟在于天变。则其可不因此而益加敬畏之诚乎。雷以震之。风以继之。天之戒告。不啻谆谆。于此而不为之大变动。则其亦已矣。天将绝之矣。敢不惕厉。易震之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程子传之曰。震来而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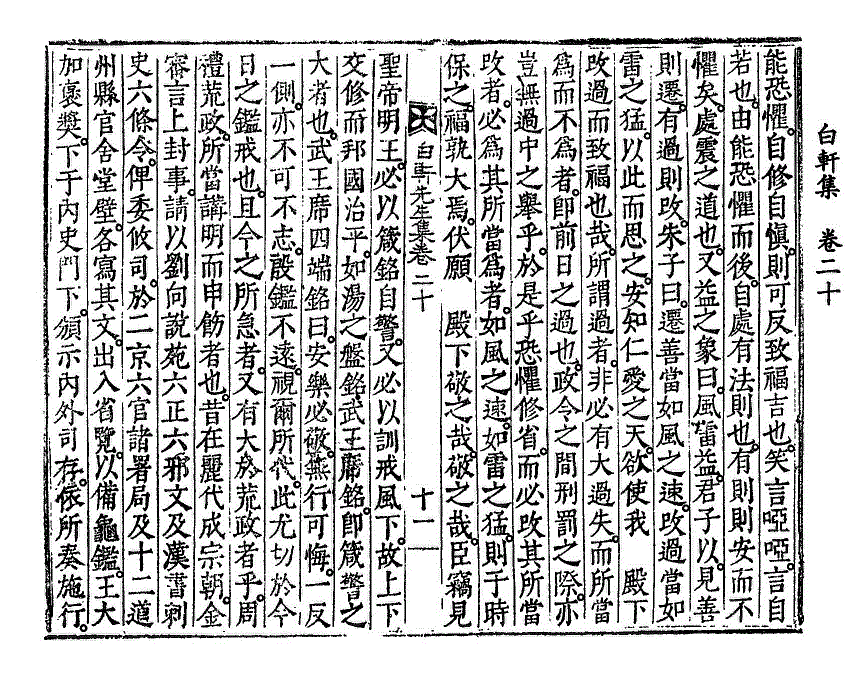 能恐惧。自修自慎。则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哑哑。言自若也。由能恐惧而后。自处有法则也。有则则安而不惧矣。处震之道也。又益之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朱子曰。迁善当如风之速。改过当如雷之猛。以此而思之。安知仁爱之天。欲使我 殿下改过而致福也哉。所谓过者。非必有大过失。而所当为而不为者。即前日之过也。政令之间刑罚之际。亦岂无过中之举乎。于是乎恐惧修省。而必改其所当改者。必为其所当为者。如风之速。如雷之猛。则于时保之。福孰大焉。伏愿 殿下敬之哉。敬之哉。臣窃见圣帝明王。必以箴铭自警。又必以训戒风下。故上下交修而邦国治平。如汤之盘铭,武王席铭。即箴警之大者也。武王席四端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不志。殷鉴不远。视尔所代。此尤切于今日之鉴戒也。且今之所急者。又有大于荒政者乎。周礼荒政。所当讲明而申饬者也。昔在丽代成宗朝。金审言上封事。请以刘向说苑六正六邪文及汉书刺史六条令。俾委攸司。于二京六官诸署局及十二道州县官舍堂壁。各写其文。出入省览。以备龟鉴。王大加褒奖。下于内史门下。颁示内外司存。依所奏施行。
能恐惧。自修自慎。则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哑哑。言自若也。由能恐惧而后。自处有法则也。有则则安而不惧矣。处震之道也。又益之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朱子曰。迁善当如风之速。改过当如雷之猛。以此而思之。安知仁爱之天。欲使我 殿下改过而致福也哉。所谓过者。非必有大过失。而所当为而不为者。即前日之过也。政令之间刑罚之际。亦岂无过中之举乎。于是乎恐惧修省。而必改其所当改者。必为其所当为者。如风之速。如雷之猛。则于时保之。福孰大焉。伏愿 殿下敬之哉。敬之哉。臣窃见圣帝明王。必以箴铭自警。又必以训戒风下。故上下交修而邦国治平。如汤之盘铭,武王席铭。即箴警之大者也。武王席四端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不志。殷鉴不远。视尔所代。此尤切于今日之鉴戒也。且今之所急者。又有大于荒政者乎。周礼荒政。所当讲明而申饬者也。昔在丽代成宗朝。金审言上封事。请以刘向说苑六正六邪文及汉书刺史六条令。俾委攸司。于二京六官诸署局及十二道州县官舍堂壁。各写其文。出入省览。以备龟鉴。王大加褒奖。下于内史门下。颁示内外司存。依所奏施行。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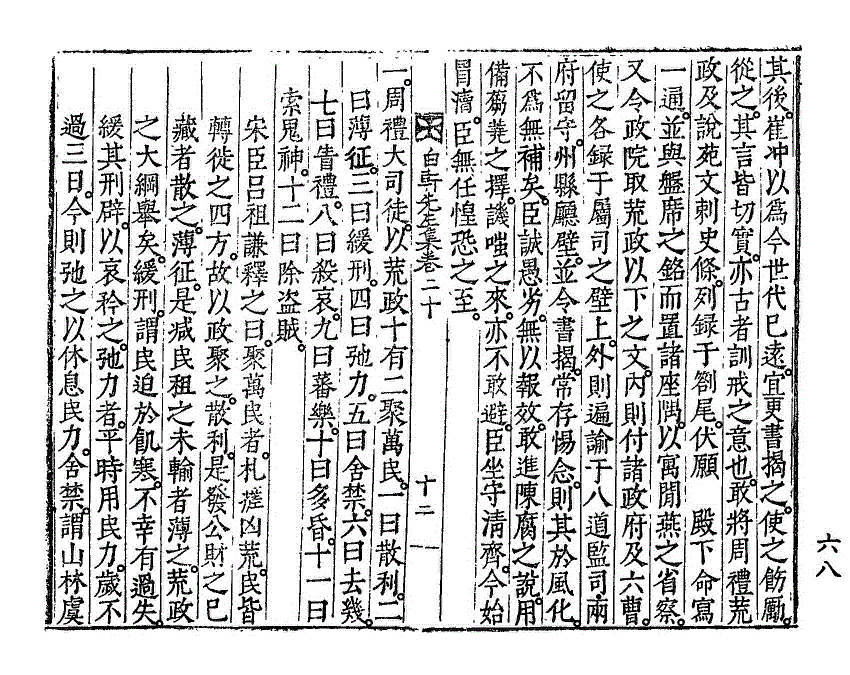 其后。崔冲以为今世代已远。宜更书揭之。使之饬励。从之。其言皆切实。亦古者训戒之意也。敢将周礼荒政及说苑文刺史条。列录于劄尾。伏愿 殿下命写一通。并与盘席之铭而置诸座隅。以寓閒燕之省察。又令政院取荒政以下之文。内则付诸政府及六曹。使之各录于属司之壁上。外则遍谕于八道监司,两府留守。州县厅壁。并令书揭。常存惕念。则其于风化。不为无补矣。臣诚愚劣。无以报效。敢进陈腐之说。用备刍荛之择。讥嗤之来。亦不敢避。臣坐守清齐。今始冒渎。臣无任惶恐之至。
其后。崔冲以为今世代已远。宜更书揭之。使之饬励。从之。其言皆切实。亦古者训戒之意也。敢将周礼荒政及说苑文刺史条。列录于劄尾。伏愿 殿下命写一通。并与盘席之铭而置诸座隅。以寓閒燕之省察。又令政院取荒政以下之文。内则付诸政府及六曹。使之各录于属司之壁上。外则遍谕于八道监司,两府留守。州县厅壁。并令书揭。常存惕念。则其于风化。不为无补矣。臣诚愚劣。无以报效。敢进陈腐之说。用备刍荛之择。讥嗤之来。亦不敢避。臣坐守清齐。今始冒渎。臣无任惶恐之至。一。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
宋臣吕祖谦释之曰。聚万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转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发公财之已藏者散之。薄征。是减民租之未输者薄之。荒政之大纲举矣。缓刑。谓民迫于饥寒。不幸有过失。缓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时用民力。岁不过三日。今则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谓山林虞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9H 页
 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几。谓去关防之讥察。使百货流通。商贾来市。此是救荒之要术。眚礼。谓凡礼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币无牲之类。杀哀。谓凡丧纪之节。一皆减损。专理会荒政。蕃乐。谓岁荒民饥。当忧民之忧。所以闭藏乐器不作。多昏。谓凶荒之年。杀礼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谓靡神不举。并走群望之类。前既说缓刑。又说除盗贼。是经权皆举。处不幸民有过。固可哀矜。至于奸民。亦有伺变窃发者。凶荒之岁。民心易动。一夫叫呼。万夫皆集。故以除盗贼终之。以止乱之萌。大抵周礼虽分职。然其关节脉理。皆相应耳。如散利。须考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财赋之官。如薄征。须考九职,九赋,九贡。如缓刑。须考司寇,士师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参观遍观然后可知。
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几。谓去关防之讥察。使百货流通。商贾来市。此是救荒之要术。眚礼。谓凡礼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币无牲之类。杀哀。谓凡丧纪之节。一皆减损。专理会荒政。蕃乐。谓岁荒民饥。当忧民之忧。所以闭藏乐器不作。多昏。谓凶荒之年。杀礼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谓靡神不举。并走群望之类。前既说缓刑。又说除盗贼。是经权皆举。处不幸民有过。固可哀矜。至于奸民。亦有伺变窃发者。凶荒之岁。民心易动。一夫叫呼。万夫皆集。故以除盗贼终之。以止乱之萌。大抵周礼虽分职。然其关节脉理。皆相应耳。如散利。须考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财赋之官。如薄征。须考九职,九赋,九贡。如缓刑。须考司寇,士师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参观遍观然后可知。弃时曰。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几。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为先。则其关系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则民不聚。虽有眚礼,蕃乐,杀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实惠及民。
一。说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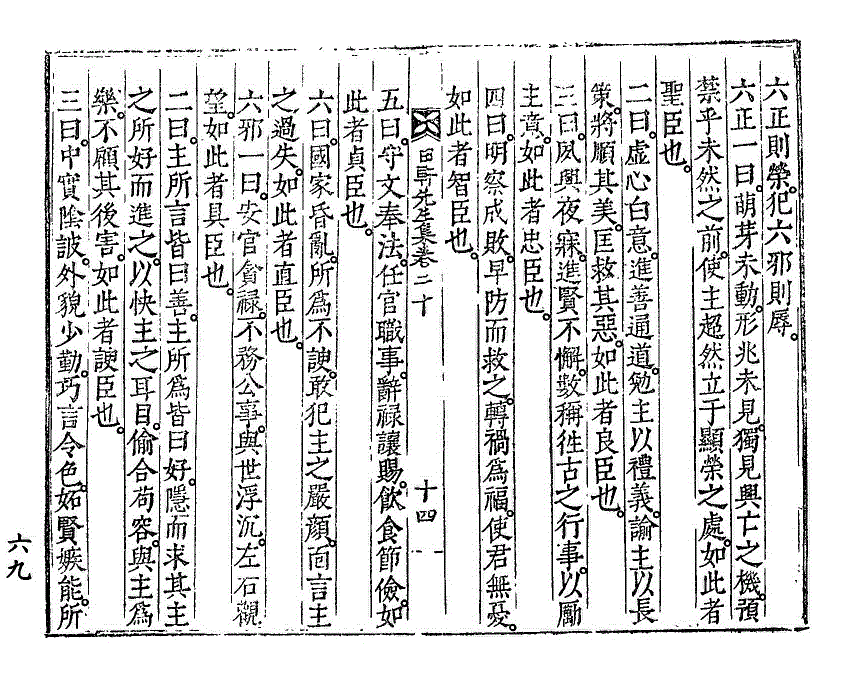 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
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独见兴亡之机。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励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转祸为福。使君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沈。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好。隐而求其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三曰。中实阴诐。外貌少勤。巧言令色。妒贤嫉能。所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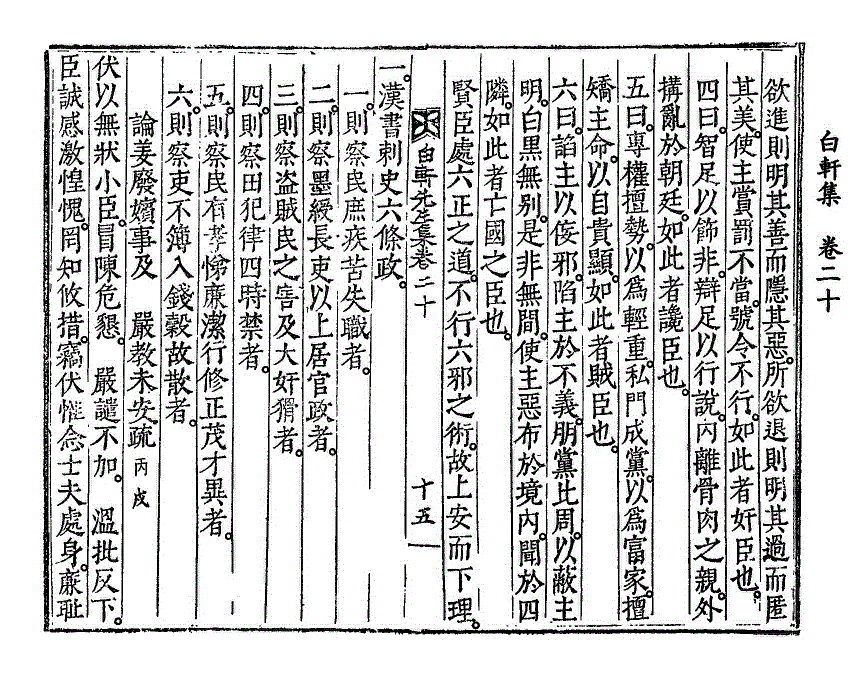 欲进则明其善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欲进则明其善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搆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五曰。专权擅势。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为富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
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
一。汉书刺史六条政。
一。则察民庶疾苦失职者。
二。则察墨绶长吏以上居官政者。
三。则察盗贼民之害及大奸猾者。
四。则察田犯律四时禁者。
五。则察民有孝悌廉洁行修正茂才异者。
六。则察吏不簿入钱谷故散者。
论姜废嫔事及 严教未安疏(丙戌)
伏以无状小臣。冒陈危恳。 严谴不加。 温批反下。臣诚感激惶愧。罔知攸措。窃伏惟念士夫处身。廉耻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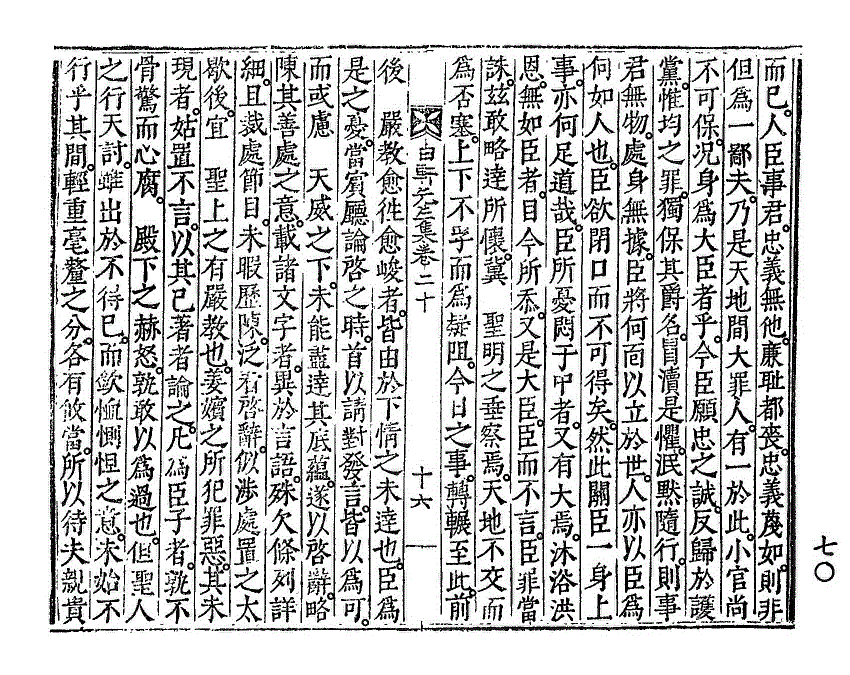 而已。人臣事君。忠义无他。廉耻都丧。忠义蔑如。则非但为一鄙夫。乃是天地间大罪人。有一于此。小官尚不可保。况身为大臣者乎。今臣愿忠之诚。反归于护党。惟均之罪。独保其爵名。冒渎是惧。泯默随行。则事君无物。处身无据。臣将何面以立于世。人亦以臣为何如人也。臣欲闭口而不可得矣。然此关臣一身上事。亦何足道哉。臣所忧闷于中者。又有大焉。沐浴洪恩。无如臣者。目今所忝。又是大臣。臣而不言。臣罪当诛。玆敢略达所怀。冀 圣明之垂察焉。天地不交而为否塞。上下不孚而为疑阻。今日之事。转辗至此。前后 严教愈往愈峻者。皆由于下情之未达也。臣为是之忧。当宾厅论启之时。首以请对发言。皆以为可。而或虑 天威之下。未能尽达其底蕴。遂以启辞。略陈其善处之意。载诸文字者。异于言语。殊欠条列详细。且裁处节目。未暇历陈。泛看启辞。似涉处置之太歇后。宜 圣上之有严教也。姜嫔之所犯罪恶。其未现者。姑置不言。以其已著者论之。凡为臣子者。孰不骨惊而心腐。 殿下之赫怒。孰敢以为过也。但圣人之行天讨。虽出于不得已。而钦恤恻怛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间。轻重毫釐之分。各有攸当。所以待夫亲贵
而已。人臣事君。忠义无他。廉耻都丧。忠义蔑如。则非但为一鄙夫。乃是天地间大罪人。有一于此。小官尚不可保。况身为大臣者乎。今臣愿忠之诚。反归于护党。惟均之罪。独保其爵名。冒渎是惧。泯默随行。则事君无物。处身无据。臣将何面以立于世。人亦以臣为何如人也。臣欲闭口而不可得矣。然此关臣一身上事。亦何足道哉。臣所忧闷于中者。又有大焉。沐浴洪恩。无如臣者。目今所忝。又是大臣。臣而不言。臣罪当诛。玆敢略达所怀。冀 圣明之垂察焉。天地不交而为否塞。上下不孚而为疑阻。今日之事。转辗至此。前后 严教愈往愈峻者。皆由于下情之未达也。臣为是之忧。当宾厅论启之时。首以请对发言。皆以为可。而或虑 天威之下。未能尽达其底蕴。遂以启辞。略陈其善处之意。载诸文字者。异于言语。殊欠条列详细。且裁处节目。未暇历陈。泛看启辞。似涉处置之太歇后。宜 圣上之有严教也。姜嫔之所犯罪恶。其未现者。姑置不言。以其已著者论之。凡为臣子者。孰不骨惊而心腐。 殿下之赫怒。孰敢以为过也。但圣人之行天讨。虽出于不得已。而钦恤恻怛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间。轻重毫釐之分。各有攸当。所以待夫亲贵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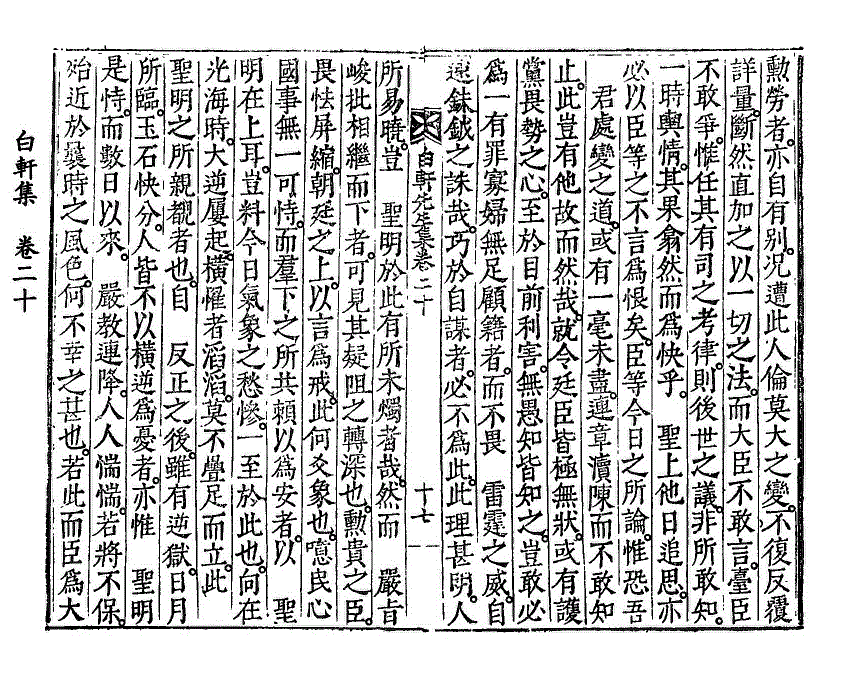 勋劳者。亦自有别。况遭此人伦莫大之变。不复反覆详量。断然直加之以一切之法。而大臣不敢言。台臣不敢争。惟任其有司之考律。则后世之议。非所敢知。一时舆情。其果翕然而为快乎。 圣上他日追思。亦必以臣等之不言为恨矣。臣等今日之所论。惟恐吾 君处变之道。或有一毫未尽。连章渎陈而不敢知止。此岂有他故而然哉。就令廷臣皆极无状。或有护党畏势之心。至于目前利害。无愚知皆知之。岂敢必为一有罪寡妇无足顾籍者。而不畏 雷霆之威。自速鈇钺之诛哉。巧于自谋者。必不为此。此理甚明。人所易晓。岂 圣明于此有所未烛者哉。然而 严旨峻批相继而下者。可见其疑阻之转深也。勋贵之臣。畏怯屏缩。朝廷之上。以言为戒。此何爻象也。噫民心国事无一可恃。而群下之所共赖以为安者。以 圣明在上耳。岂料今日气象之愁惨。一至于此也。向在光海时。大逆屡起。横罹者滔滔。莫不叠足而立。此 圣明之所亲睹者也。自 反正之后。虽有逆狱。日月所临。玉石快分。人皆不以横逆为忧者。亦惟 圣明是恃。而数日以来。 严教连降。人人惴惴。若将不保。殆近于曩时之风色。何不幸之甚也。若此而臣为大
勋劳者。亦自有别。况遭此人伦莫大之变。不复反覆详量。断然直加之以一切之法。而大臣不敢言。台臣不敢争。惟任其有司之考律。则后世之议。非所敢知。一时舆情。其果翕然而为快乎。 圣上他日追思。亦必以臣等之不言为恨矣。臣等今日之所论。惟恐吾 君处变之道。或有一毫未尽。连章渎陈而不敢知止。此岂有他故而然哉。就令廷臣皆极无状。或有护党畏势之心。至于目前利害。无愚知皆知之。岂敢必为一有罪寡妇无足顾籍者。而不畏 雷霆之威。自速鈇钺之诛哉。巧于自谋者。必不为此。此理甚明。人所易晓。岂 圣明于此有所未烛者哉。然而 严旨峻批相继而下者。可见其疑阻之转深也。勋贵之臣。畏怯屏缩。朝廷之上。以言为戒。此何爻象也。噫民心国事无一可恃。而群下之所共赖以为安者。以 圣明在上耳。岂料今日气象之愁惨。一至于此也。向在光海时。大逆屡起。横罹者滔滔。莫不叠足而立。此 圣明之所亲睹者也。自 反正之后。虽有逆狱。日月所临。玉石快分。人皆不以横逆为忧者。亦惟 圣明是恃。而数日以来。 严教连降。人人惴惴。若将不保。殆近于曩时之风色。何不幸之甚也。若此而臣为大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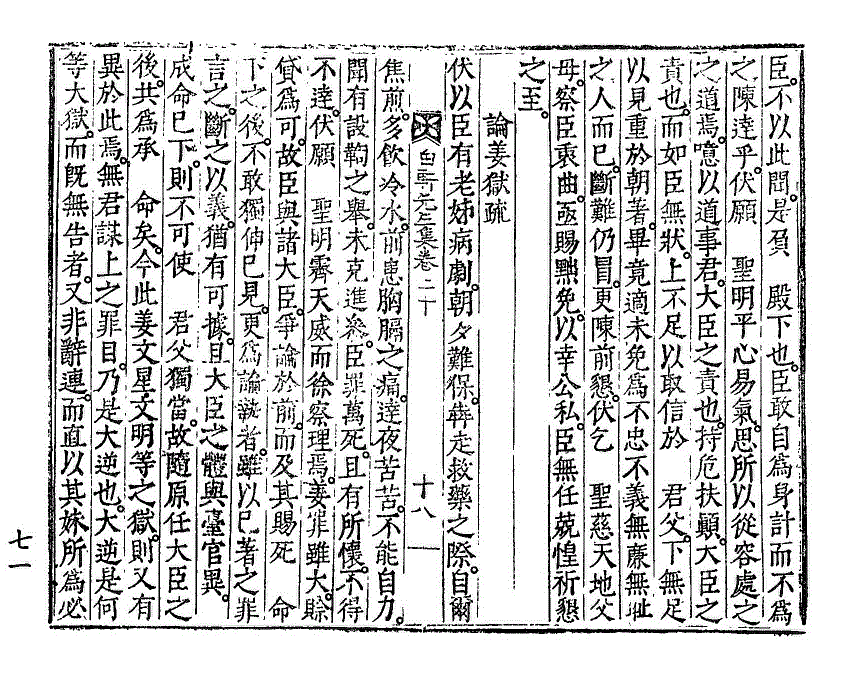 臣。不以此闻。是负 殿下也。臣敢自为身计而不为之陈达乎。伏愿 圣明平心易气。思所以从容处之之道焉。噫以道事君。大臣之责也。持危扶颠。大臣之责也。而如臣无状。上不足以取信于 君父。下无足以见重于朝著。毕竟适未免为不忠不义无廉无耻之人而已。断难仍冒。更陈前恳。伏乞 圣慈天地父母。察臣衷曲。亟赐黜免。以幸公私。臣无任兢惶祈恳之至。
臣。不以此闻。是负 殿下也。臣敢自为身计而不为之陈达乎。伏愿 圣明平心易气。思所以从容处之之道焉。噫以道事君。大臣之责也。持危扶颠。大臣之责也。而如臣无状。上不足以取信于 君父。下无足以见重于朝著。毕竟适未免为不忠不义无廉无耻之人而已。断难仍冒。更陈前恳。伏乞 圣慈天地父母。察臣衷曲。亟赐黜免。以幸公私。臣无任兢惶祈恳之至。论姜狱疏
伏以臣有老姊病剧。朝夕难保。奔走救药之际。自尔焦煎。多饮冷水。前患胸膈之痛。达夜苦苦。不能自力。闻有设鞫之举。未克进参。臣罪万死。且有所怀。不得不达。伏愿 圣明霁天威而徐察理焉。姜罪虽大。赊贷为可。故臣与诸大臣。争论于前。而及其赐死 命下之后。不敢独伸己见。更为论执者。虽以已著之罪言之。断之以义。犹有可据。且大臣之体与台官异。 成命已下。则不可使 君父独当。故随原任大臣之后。共为承 命矣。今此姜文星,文明等之狱。则又有异于此焉。无君谋上之罪目。乃是大逆也。大逆是何等大狱。而既无告者。又非辞连。而直以其妹所为必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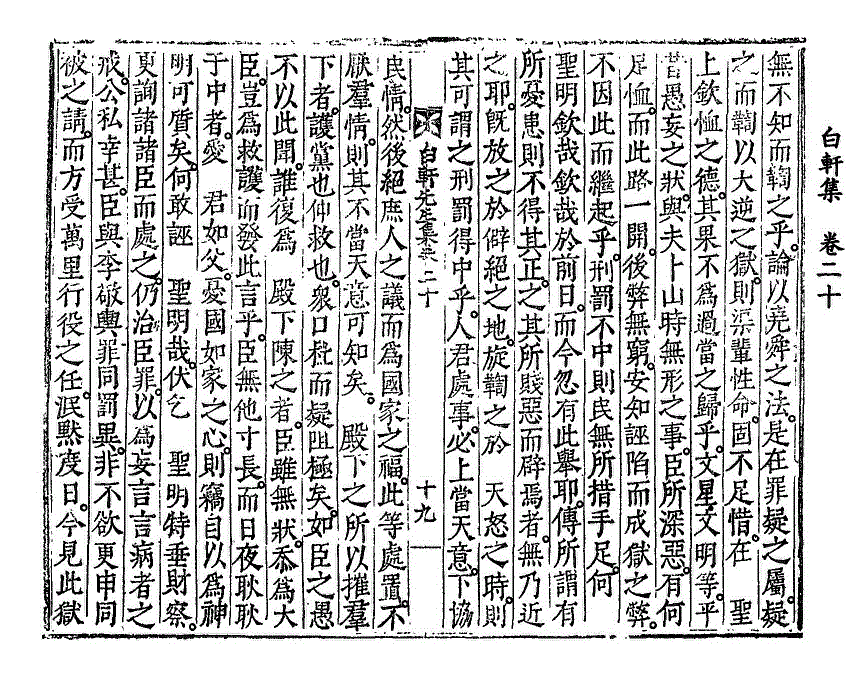 无不知而鞫之乎。论以尧舜之法。是在罪疑之属。疑之而鞫以大逆之狱。则渠辈性命。固不足惜。在 圣上钦恤之德。其果不为过当之归乎。文星,文明等。平昔愚妄之状。与夫卜山时无形之事。臣所深恶。有何足恤。而此路一开。后弊无穷。安知诬陷而成狱之弊。不因此而继起乎。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何 圣明钦哉钦哉于前日。而今忽有此举耶。传所谓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之其所贱恶而辟焉者。无乃近之耶。既放之于僻绝之地。旋鞫之于 天怒之时。则其可谓之刑罚得中乎。人君处事。必上当天意。下协民情。然后绝庶人之议而为国家之福。此等处置。不厌群情。则其不当天意可知矣。 殿下之所以摧群下者。护党也伸救也。众口杜而疑阻极矣。如臣之愚不以此闻。谁复为 殿下陈之者。臣虽无状。忝为大臣。岂为救护而发此言乎。臣无他寸长。而日夜耿耿于中者。爱 君如父。忧国如家之心。则窃自以为神明可质矣。何敢诬 圣明哉。伏乞 圣明特垂财察。更询诸诸臣而处之。仍治臣罪。以为妄言言病者之戒。公私幸甚。臣与李敬舆罪同罚异。非不欲更申同被之请。而方受万里行役之任。泯默度日。今见此狱
无不知而鞫之乎。论以尧舜之法。是在罪疑之属。疑之而鞫以大逆之狱。则渠辈性命。固不足惜。在 圣上钦恤之德。其果不为过当之归乎。文星,文明等。平昔愚妄之状。与夫卜山时无形之事。臣所深恶。有何足恤。而此路一开。后弊无穷。安知诬陷而成狱之弊。不因此而继起乎。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何 圣明钦哉钦哉于前日。而今忽有此举耶。传所谓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之其所贱恶而辟焉者。无乃近之耶。既放之于僻绝之地。旋鞫之于 天怒之时。则其可谓之刑罚得中乎。人君处事。必上当天意。下协民情。然后绝庶人之议而为国家之福。此等处置。不厌群情。则其不当天意可知矣。 殿下之所以摧群下者。护党也伸救也。众口杜而疑阻极矣。如臣之愚不以此闻。谁复为 殿下陈之者。臣虽无状。忝为大臣。岂为救护而发此言乎。臣无他寸长。而日夜耿耿于中者。爱 君如父。忧国如家之心。则窃自以为神明可质矣。何敢诬 圣明哉。伏乞 圣明特垂财察。更询诸诸臣而处之。仍治臣罪。以为妄言言病者之戒。公私幸甚。臣与李敬舆罪同罚异。非不欲更申同被之请。而方受万里行役之任。泯默度日。今见此狱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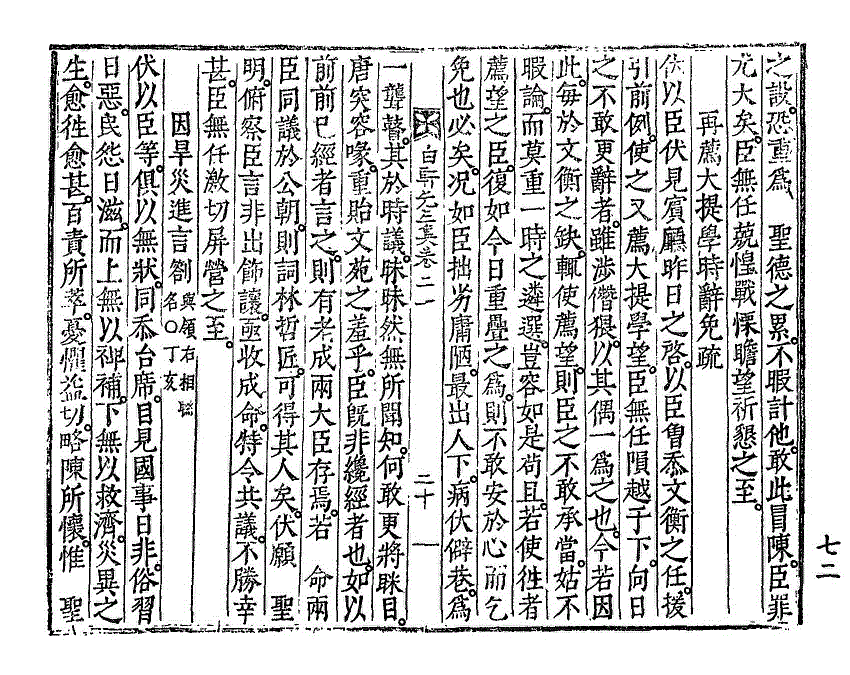 之设。恐重为 圣德之累。不暇计他。敢此冒陈。臣罪尤大矣。臣无任兢惶战慄瞻望祈恳之至。
之设。恐重为 圣德之累。不暇计他。敢此冒陈。臣罪尤大矣。臣无任兢惶战慄瞻望祈恳之至。再荐大提学时辞免疏
伏以臣伏见宾厅昨日之启。以臣曾忝文衡之任。援引前例。使之又荐大提学望。臣无任陨越于下。向日之不敢更辞者。虽涉僭猥。以其偶一为之也。今若因此。每于文衡之缺。辄使荐望。则臣之不敢承当。姑不暇论。而莫重一时之遴选。岂容如是苟且。若使往者荐望之臣。复如今日重叠之为。则不敢安于心而乞免也必矣。况如臣拙劣庸陋。最出人下。病伏僻巷。为一聋瞽。其于时议。昧昧然无所闻知。何敢更将眯目。唐突容喙。重贻文苑之羞乎。臣既非才经者也。如以前前已经者言之。则有老成两大臣存焉。若 命两臣同议于公朝。则词林哲匠。可得其人矣。伏愿 圣明。俯察臣言非出饰让。亟收成命。特令共议。不胜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因旱灾进言劄(与领右相联名○丁亥)
伏以臣等。俱以无状。同忝台席。目见国事日非。俗习日恶。民怨日滋。而上无以裨补。下无以救济。灾异之生。愈往愈甚。百责所萃。忧惧益切。略陈所怀。惟 圣
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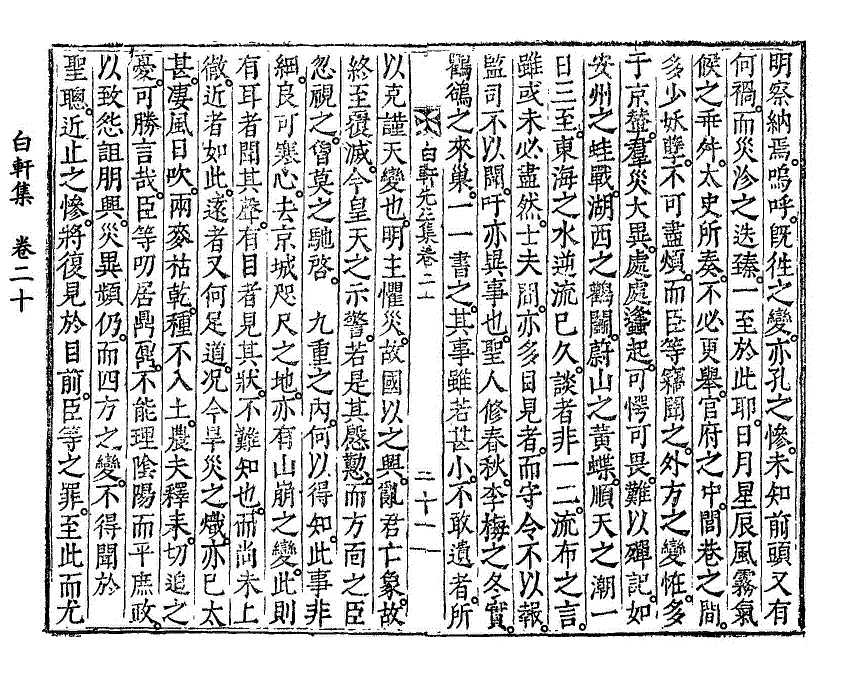 明察纳焉。呜呼。既往之变。亦孔之惨。未知前头又有何祸。而灾沴之迭臻。一至于此耶。日月星辰风雾气候之乖舛。太史所奏。不必更举。官府之中。闾巷之间。多少妖孽。不可尽烦。而臣等窃闻之。外方之变怪。多于京辇。群灾大异。处处蜂起。可愕可畏。难以殚记。如安州之蛙战。湖西之鹳斗。蔚山之黄蝶。顺天之潮一日三至。东海之水逆流已久。谈者非一二。流布之言。虽或未必尽然。士夫间。亦多目见者。而守令不以报。监司不以闻。吁亦异事也。圣人修春秋。李梅之冬实。鸲鹆之来巢。一一书之。其事虽若甚小。不敢遗者。所以克谨天变也。明主惧灾。故国以之兴。乱君亡象。故终至覆灭。今皇天之示警。若是其慇勤。而方面之臣忽视之。曾莫之驰启。 九重之内。何以得知。此事非细。良可寒心。去京城咫尺之地。亦有山崩之变。此则有耳者闻其声。有目者见其状。不难知也。而尚未上彻。近者如此。远者又何足道。况今旱灾之炽。亦已太甚。凄风日吹。两麦枯乾。种不入土。农夫释耒。切迫之忧。可胜言哉。臣等叨居鼎鼐。不能理阴阳而平庶政。以致怨诅朋兴。灾异频仍。而四方之变。不得闻于 圣聪。近止之惨。将复见于目前。臣等之罪。至此而尤
明察纳焉。呜呼。既往之变。亦孔之惨。未知前头又有何祸。而灾沴之迭臻。一至于此耶。日月星辰风雾气候之乖舛。太史所奏。不必更举。官府之中。闾巷之间。多少妖孽。不可尽烦。而臣等窃闻之。外方之变怪。多于京辇。群灾大异。处处蜂起。可愕可畏。难以殚记。如安州之蛙战。湖西之鹳斗。蔚山之黄蝶。顺天之潮一日三至。东海之水逆流已久。谈者非一二。流布之言。虽或未必尽然。士夫间。亦多目见者。而守令不以报。监司不以闻。吁亦异事也。圣人修春秋。李梅之冬实。鸲鹆之来巢。一一书之。其事虽若甚小。不敢遗者。所以克谨天变也。明主惧灾。故国以之兴。乱君亡象。故终至覆灭。今皇天之示警。若是其慇勤。而方面之臣忽视之。曾莫之驰启。 九重之内。何以得知。此事非细。良可寒心。去京城咫尺之地。亦有山崩之变。此则有耳者闻其声。有目者见其状。不难知也。而尚未上彻。近者如此。远者又何足道。况今旱灾之炽。亦已太甚。凄风日吹。两麦枯乾。种不入土。农夫释耒。切迫之忧。可胜言哉。臣等叨居鼎鼐。不能理阴阳而平庶政。以致怨诅朋兴。灾异频仍。而四方之变。不得闻于 圣聪。近止之惨。将复见于目前。臣等之罪。至此而尤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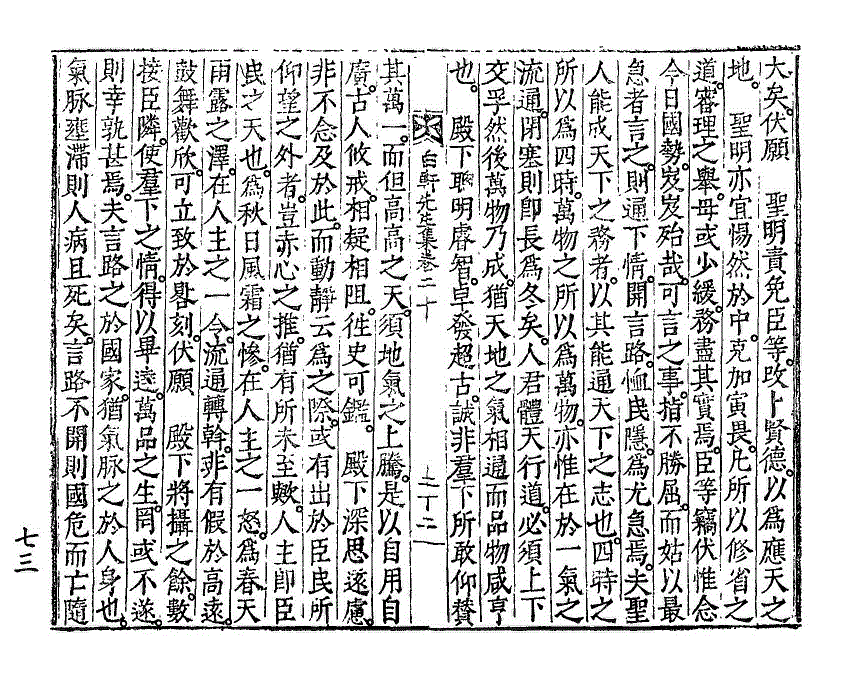 大矣。伏愿 圣明责免臣等。改卜贤德。以为应天之地。 圣明亦宜惕然于中。克加寅畏。凡所以修省之道。审理之举。毋或少缓。务尽其实焉。臣等窃伏惟念今日国势。岌岌殆哉。可言之事。指不胜屈。而姑以最急者言之。则通下情。开言路。恤民隐。为尤急焉。夫圣人能成天下之务者。以其能通天下之志也。四时之所以为四时。万物之所以为万物。亦惟在于一气之流通。闭塞则即长为冬矣。人君体天行道。必须上下交孚然后万物乃成。犹天地之气相通而品物咸亨也。 殿下聪明睿智。卓发超古。诚非群下所敢仰赞其万一。而但高高之天。须地气之上腾。是以自用自广。古人攸戒。相疑相阻。往史可鉴。 殿下深思远虑。非不念及于此。而动静云为之际。或有出于臣民所仰望之外者。岂赤心之推。犹有所未至欤。人主即臣民之天也。为秋日风霜之惨。在人主之一怒。为春天雨露之泽。在人主之一令。流通转斡。非有假于高远。鼓舞欢欣。可立致于晷刻。伏愿 殿下将摄之馀。数接臣邻。使群下之情。得以毕达。万品之生。罔或不遂。则幸孰甚焉。夫言路之于国家。犹气脉之于人身也。气脉壅滞则人病且死矣。言路不开则国危而亡随
大矣。伏愿 圣明责免臣等。改卜贤德。以为应天之地。 圣明亦宜惕然于中。克加寅畏。凡所以修省之道。审理之举。毋或少缓。务尽其实焉。臣等窃伏惟念今日国势。岌岌殆哉。可言之事。指不胜屈。而姑以最急者言之。则通下情。开言路。恤民隐。为尤急焉。夫圣人能成天下之务者。以其能通天下之志也。四时之所以为四时。万物之所以为万物。亦惟在于一气之流通。闭塞则即长为冬矣。人君体天行道。必须上下交孚然后万物乃成。犹天地之气相通而品物咸亨也。 殿下聪明睿智。卓发超古。诚非群下所敢仰赞其万一。而但高高之天。须地气之上腾。是以自用自广。古人攸戒。相疑相阻。往史可鉴。 殿下深思远虑。非不念及于此。而动静云为之际。或有出于臣民所仰望之外者。岂赤心之推。犹有所未至欤。人主即臣民之天也。为秋日风霜之惨。在人主之一怒。为春天雨露之泽。在人主之一令。流通转斡。非有假于高远。鼓舞欢欣。可立致于晷刻。伏愿 殿下将摄之馀。数接臣邻。使群下之情。得以毕达。万品之生。罔或不遂。则幸孰甚焉。夫言路之于国家。犹气脉之于人身也。气脉壅滞则人病且死矣。言路不开则国危而亡随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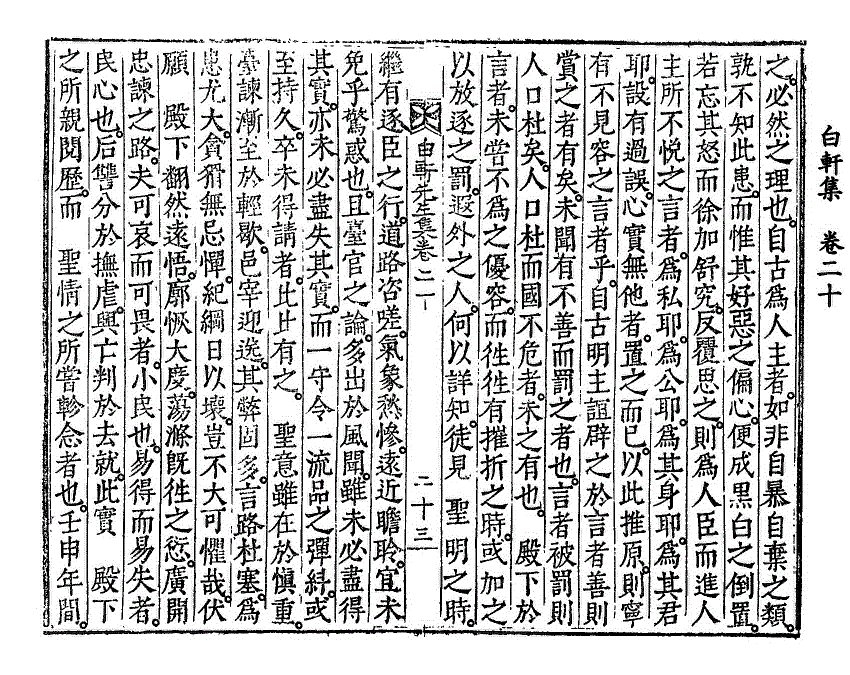 之。必然之理也。自古为人主者。如非自暴自弃之类。孰不知此患。而惟其好恶之偏心。便成黑白之倒置。若忘其怒而徐加舒究。反覆思之。则为人臣而进人主所不悦之言者。为私耶。为公耶。为其身耶。为其君耶。设有过误。心实无他者。置之而已。以此推原。则宁有不见容之言者乎。自古明主谊辟之于言者善则赏之者有矣。未闻有不善而罚之者也。言者被罚则人口杜矣。人口杜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殿下于言者。未尝不为之优容。而往往有摧折之时。或加之以放逐之罚。遐外之人。何以详知。徒见 圣明之时。继有逐臣之行。道路咨嗟。气象愁惨。远近瞻聆。宜未免乎惊惑也。且台官之论。多出于风闻。虽未必尽得其实。亦未必尽失其实。而一守令一流品之弹纠。或至持久。卒未得请者。比比有之。 圣意虽在于慎重。台谏渐至于轻歇。邑宰迎送。其弊固多。言路杜塞。为患尤大。贪猾无忌惮。纪纲日以坏。岂不大可惧哉。伏愿 殿下翻然远悟。廓恢大度。荡涤既往之愆。广开忠谏之路。夫可哀而可畏者。小民也。易得而易失者。民心也。后雠分于抚虐。兴亡判于去就。此实 殿下之所亲阅历。而 圣情之所尝轸念者也。壬申年间。
之。必然之理也。自古为人主者。如非自暴自弃之类。孰不知此患。而惟其好恶之偏心。便成黑白之倒置。若忘其怒而徐加舒究。反覆思之。则为人臣而进人主所不悦之言者。为私耶。为公耶。为其身耶。为其君耶。设有过误。心实无他者。置之而已。以此推原。则宁有不见容之言者乎。自古明主谊辟之于言者善则赏之者有矣。未闻有不善而罚之者也。言者被罚则人口杜矣。人口杜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殿下于言者。未尝不为之优容。而往往有摧折之时。或加之以放逐之罚。遐外之人。何以详知。徒见 圣明之时。继有逐臣之行。道路咨嗟。气象愁惨。远近瞻聆。宜未免乎惊惑也。且台官之论。多出于风闻。虽未必尽得其实。亦未必尽失其实。而一守令一流品之弹纠。或至持久。卒未得请者。比比有之。 圣意虽在于慎重。台谏渐至于轻歇。邑宰迎送。其弊固多。言路杜塞。为患尤大。贪猾无忌惮。纪纲日以坏。岂不大可惧哉。伏愿 殿下翻然远悟。廓恢大度。荡涤既往之愆。广开忠谏之路。夫可哀而可畏者。小民也。易得而易失者。民心也。后雠分于抚虐。兴亡判于去就。此实 殿下之所亲阅历。而 圣情之所尝轸念者也。壬申年间。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4L 页
 圣教有曰。重利轻民。非予所尚。虽以利害言之。民生保存。乃国之大利。大哉之言。孰不感激。 圣心如此。故措诸事为之间者。无非保民之意。承流宣化分忧字牧之臣。苟能尽体 圣心。今日民生之重困。岂至于此极乎。而臣等窃闻之。外方守令。鲜克廉谨。苛政横敛恣意者有之。监司黜陟。或未尽公。随其好恶失当者有之。至于逃故族邻之弊。言之久矣。上司不能不严督。列邑不能不奉行。或徵于朽骨。或责于白地。军民之怨苦。与日俱增。村聚之流散。逐年渐多。一户之逃。一邻尽空。今岁如此。来岁如此。其终也当至于何域。外寇非畏。此甚可畏。此外狱讼之偏私。刑杖之过滥。病国害民之事。不一而足。说者以为御史之不行已久。外方之贪纵益甚。此言诚然矣。毁誉之中。实状难得。而身亲闻见。岂无参验。不法之迹。文籍可考。与夫流闻。迥然有异。大槩如有御史声息。则莫不有严惮之心。其为利益。章章明矣。虽或有奉使不当意者。岂可因噎而废食。但只察若干邑。其馀州县则虽有所闻。不得论启。殊非所以遣御史之意也。伏愿 殿下特简暗行。遍询八道之民瘼。痛祛太甚之贪吏。兼令历观风俗。搜访贤才。以备 睿览。以为登庸。则
圣教有曰。重利轻民。非予所尚。虽以利害言之。民生保存。乃国之大利。大哉之言。孰不感激。 圣心如此。故措诸事为之间者。无非保民之意。承流宣化分忧字牧之臣。苟能尽体 圣心。今日民生之重困。岂至于此极乎。而臣等窃闻之。外方守令。鲜克廉谨。苛政横敛恣意者有之。监司黜陟。或未尽公。随其好恶失当者有之。至于逃故族邻之弊。言之久矣。上司不能不严督。列邑不能不奉行。或徵于朽骨。或责于白地。军民之怨苦。与日俱增。村聚之流散。逐年渐多。一户之逃。一邻尽空。今岁如此。来岁如此。其终也当至于何域。外寇非畏。此甚可畏。此外狱讼之偏私。刑杖之过滥。病国害民之事。不一而足。说者以为御史之不行已久。外方之贪纵益甚。此言诚然矣。毁誉之中。实状难得。而身亲闻见。岂无参验。不法之迹。文籍可考。与夫流闻。迥然有异。大槩如有御史声息。则莫不有严惮之心。其为利益。章章明矣。虽或有奉使不当意者。岂可因噎而废食。但只察若干邑。其馀州县则虽有所闻。不得论启。殊非所以遣御史之意也。伏愿 殿下特简暗行。遍询八道之民瘼。痛祛太甚之贪吏。兼令历观风俗。搜访贤才。以备 睿览。以为登庸。则白轩先生集卷之二十○文稿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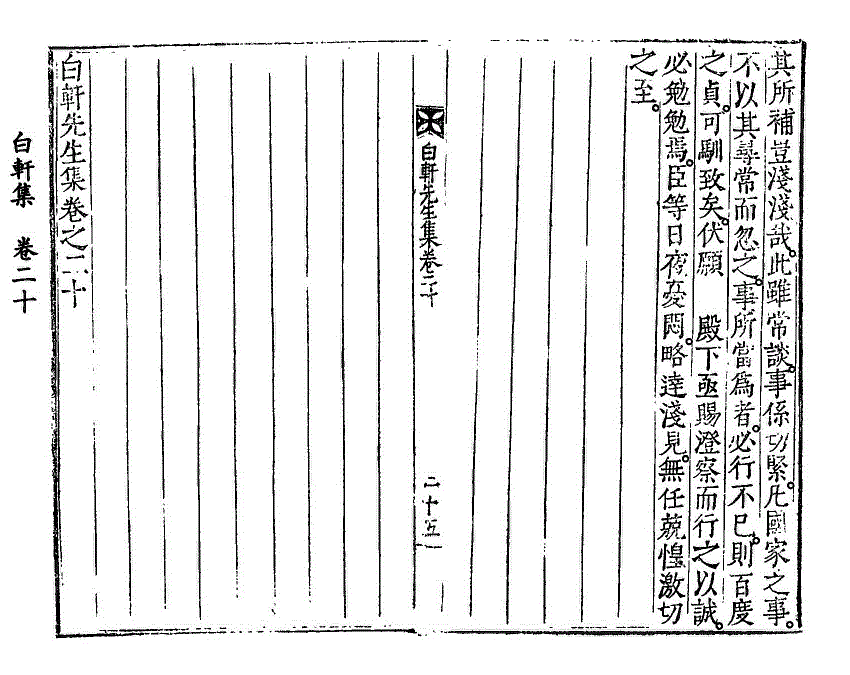 其所补岂浅浅哉。此虽常谈。事系切紧。凡国家之事。不以其寻常而忽之。事所当为者。必行不已。则百度之贞。可驯致矣。伏愿 殿下亟赐澄察而行之以诚。必勉勉焉。臣等日夜忧闷。略达浅见。无任兢惶激切之至。
其所补岂浅浅哉。此虽常谈。事系切紧。凡国家之事。不以其寻常而忽之。事所当为者。必行不已。则百度之贞。可驯致矣。伏愿 殿下亟赐澄察而行之以诚。必勉勉焉。臣等日夜忧闷。略达浅见。无任兢惶激切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