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杂著(十一首)
杂著(十一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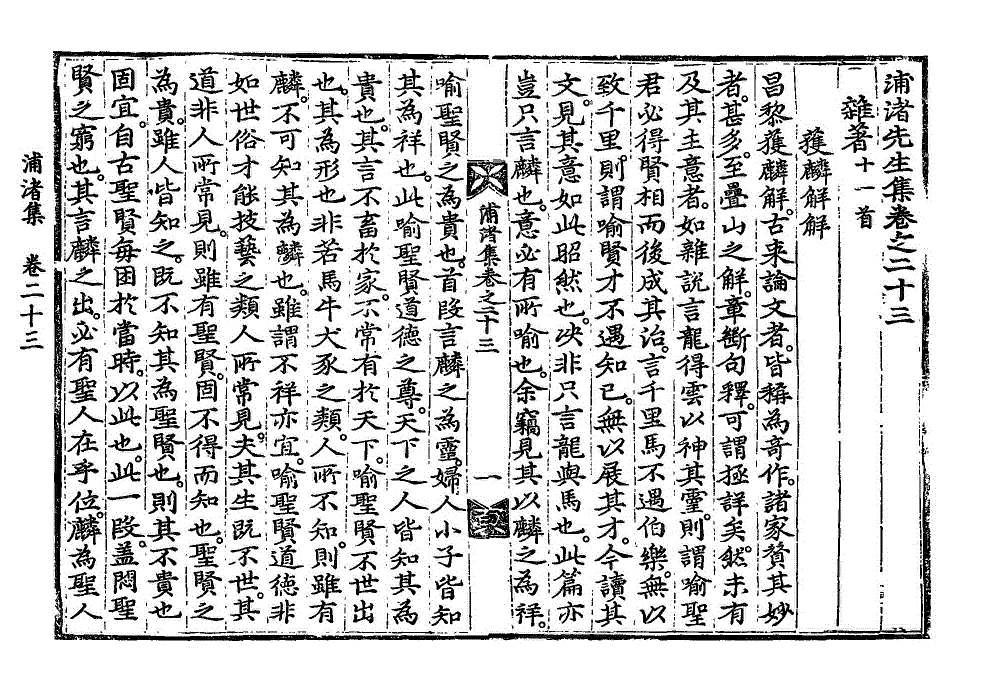 获麟解解
获麟解解昌黎获麟解。古来论文者。皆称为奇作。诸家赞其妙者。甚多。至叠山之解。章断句释。可谓极详矣。然未有及其主意者。如杂说言龙得云以神其灵。则谓喻圣君必得贤相而后成其治。言千里马不遇伯乐。无以致千里。则谓喻贤才不遇知己。无以展其才。今读其文。见其意如此昭然也。决非只言龙与马也。此篇亦岂只言麟也。意必有所喻也。余窃见其以麟之为祥。喻圣贤之为贵也。首段言麟之为灵。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此喻圣贤道德之尊。天下之人皆知其为贵也。其言不畜于家。不常有于天下。喻圣贤不世出也。其为形也非若马牛犬豕之类。人所不知。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虽谓不祥亦宜。喻圣贤道德非如世俗才能技艺之类人所常见。夫其生既不世。其道非人所常见。则虽有圣贤。固不得而知也。圣贤之为贵。虽人皆知之。既不知其为圣贤也。则其不贵也固宜。自古圣贤每困于当时。以此也。此一段。盖闷圣贤之穷也。其言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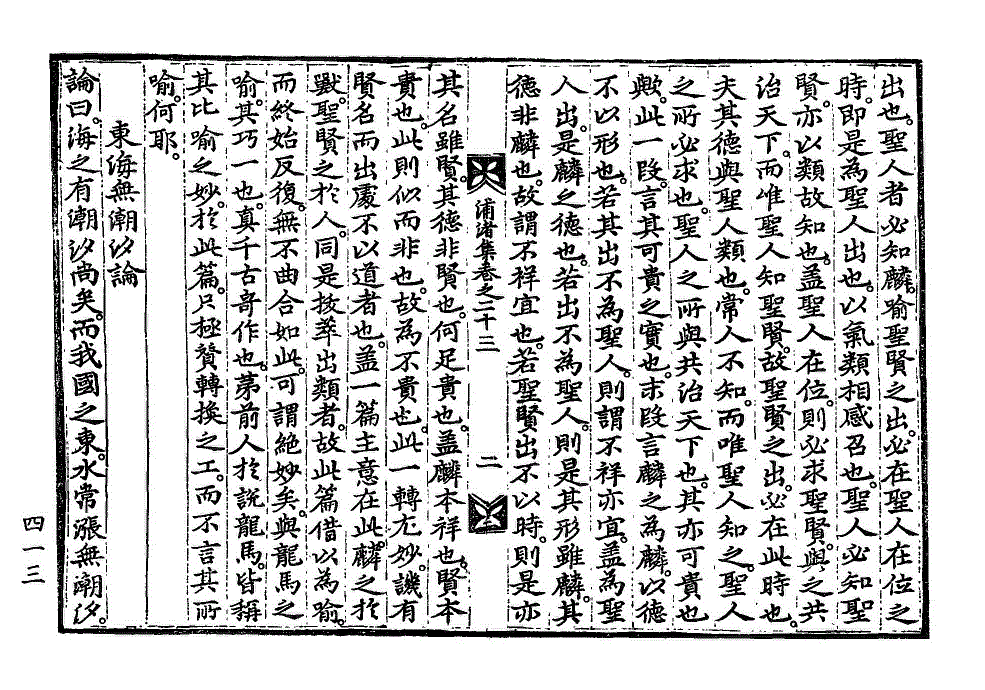 出也。圣人者必知麟。喻圣贤之出。必在圣人在位之时。即是为圣人出也。以气类相感召也。圣人必知圣贤。亦以类故知也。盖圣人在位。则必求圣贤。与之共治天下。而唯圣人知圣贤。故圣贤之出。必在此时也。夫其德与圣人类也。常人不知。而唯圣人知之。圣人之所必求也。圣人之所与共治天下也。其亦可贵也欤。此一段。言其可贵之实也。末段言麟之为麟。以德不以形也。若其出不为圣人。则谓不祥亦宜。盖为圣人出。是麟之德也。若出不为圣人。则是其形虽麟。其德非麟也。故谓不祥宜也。若圣贤出不以时。则是亦其名虽贤。其德非贤也。何足贵也。盖麟本祥也。贤本贵也。此则似而非也。故为不贵也。此一转尤妙。讥有贤名而出处不以道者也。盖一篇主意在此。麟之于兽。圣贤之于人。同是拔萃出类者。故此篇借以为喻。而终始反复。无不曲合如此。可谓绝妙矣。与龙马之喻。其巧一也。真千古奇作也。第前人于说龙马。皆称其比喻之妙。于此篇。只极赞转换之工。而不言其所喻。何耶。
出也。圣人者必知麟。喻圣贤之出。必在圣人在位之时。即是为圣人出也。以气类相感召也。圣人必知圣贤。亦以类故知也。盖圣人在位。则必求圣贤。与之共治天下。而唯圣人知圣贤。故圣贤之出。必在此时也。夫其德与圣人类也。常人不知。而唯圣人知之。圣人之所必求也。圣人之所与共治天下也。其亦可贵也欤。此一段。言其可贵之实也。末段言麟之为麟。以德不以形也。若其出不为圣人。则谓不祥亦宜。盖为圣人出。是麟之德也。若出不为圣人。则是其形虽麟。其德非麟也。故谓不祥宜也。若圣贤出不以时。则是亦其名虽贤。其德非贤也。何足贵也。盖麟本祥也。贤本贵也。此则似而非也。故为不贵也。此一转尤妙。讥有贤名而出处不以道者也。盖一篇主意在此。麟之于兽。圣贤之于人。同是拔萃出类者。故此篇借以为喻。而终始反复。无不曲合如此。可谓绝妙矣。与龙马之喻。其巧一也。真千古奇作也。第前人于说龙马。皆称其比喻之妙。于此篇。只极赞转换之工。而不言其所喻。何耶。东海无潮汐论
论曰。海之有潮汐尚矣。而我国之东。水常涨无潮汐。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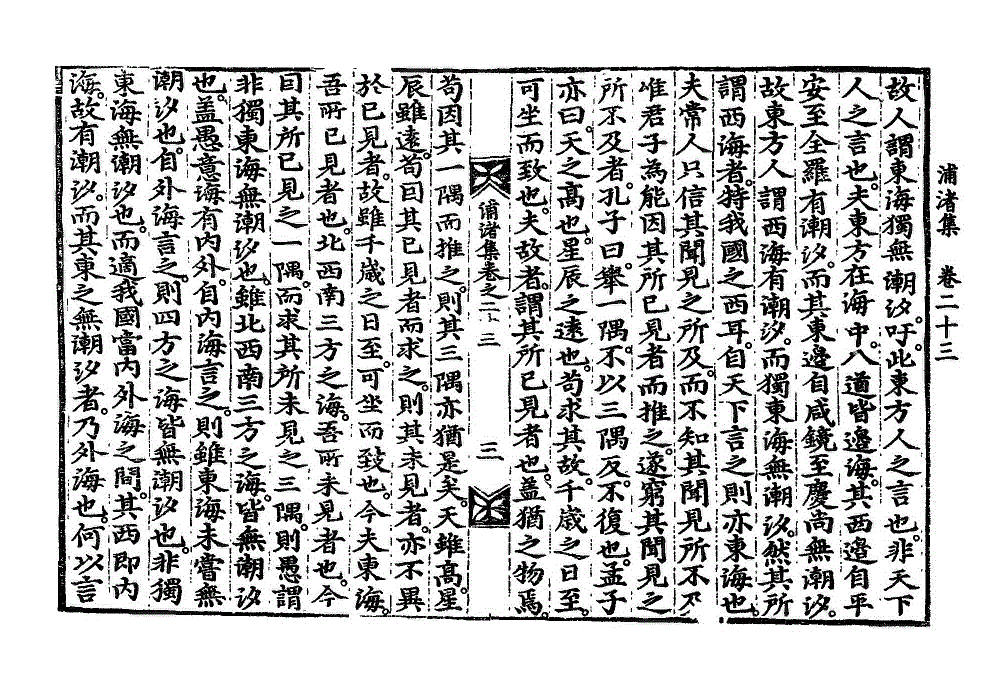 故人谓东海独无潮汐。吁。此东方人之言也。非天下人之言也。夫东方在海中。八道皆边海。其西边自平安至全罗有潮汐。而其东边自咸镜至庆尚无潮汐。故东方人谓西海有潮汐。而独东海无潮汐。然其所谓西海者。特我国之西耳。自天下言之则亦东海也。夫常人只信其闻见之所及。而不知其闻见所不及。唯君子为能因其所已见者而推之。遂穷其闻见之所不及者。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复也。孟子亦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故者。谓其所已见者也。盖犹之物焉。苟因其一隅而推之。则其三隅亦犹是矣。天虽高。星辰虽远。苟因其已见者而求之。则其未见者。亦不异于已见者。故虽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夫东海。吾所已见者也。北西南三方之海。吾所未见者也。今因其所已见之一隅。而求其所未见之三隅。则愚谓非独东海无潮汐也。虽北西南三方之海。皆无潮汐也。盖愚意海有内外。自内海言之。则虽东海未尝无潮汐也。自外海言之。则四方之海皆无潮汐也。非独东海无潮汐也。而适我国当内外海之间。其西即内海。故有潮汐。而其东之无潮汐者。乃外海也。何以言
故人谓东海独无潮汐。吁。此东方人之言也。非天下人之言也。夫东方在海中。八道皆边海。其西边自平安至全罗有潮汐。而其东边自咸镜至庆尚无潮汐。故东方人谓西海有潮汐。而独东海无潮汐。然其所谓西海者。特我国之西耳。自天下言之则亦东海也。夫常人只信其闻见之所及。而不知其闻见所不及。唯君子为能因其所已见者而推之。遂穷其闻见之所不及者。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复也。孟子亦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故者。谓其所已见者也。盖犹之物焉。苟因其一隅而推之。则其三隅亦犹是矣。天虽高。星辰虽远。苟因其已见者而求之。则其未见者。亦不异于已见者。故虽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夫东海。吾所已见者也。北西南三方之海。吾所未见者也。今因其所已见之一隅。而求其所未见之三隅。则愚谓非独东海无潮汐也。虽北西南三方之海。皆无潮汐也。盖愚意海有内外。自内海言之。则虽东海未尝无潮汐也。自外海言之。则四方之海皆无潮汐也。非独东海无潮汐也。而适我国当内外海之间。其西即内海。故有潮汐。而其东之无潮汐者。乃外海也。何以言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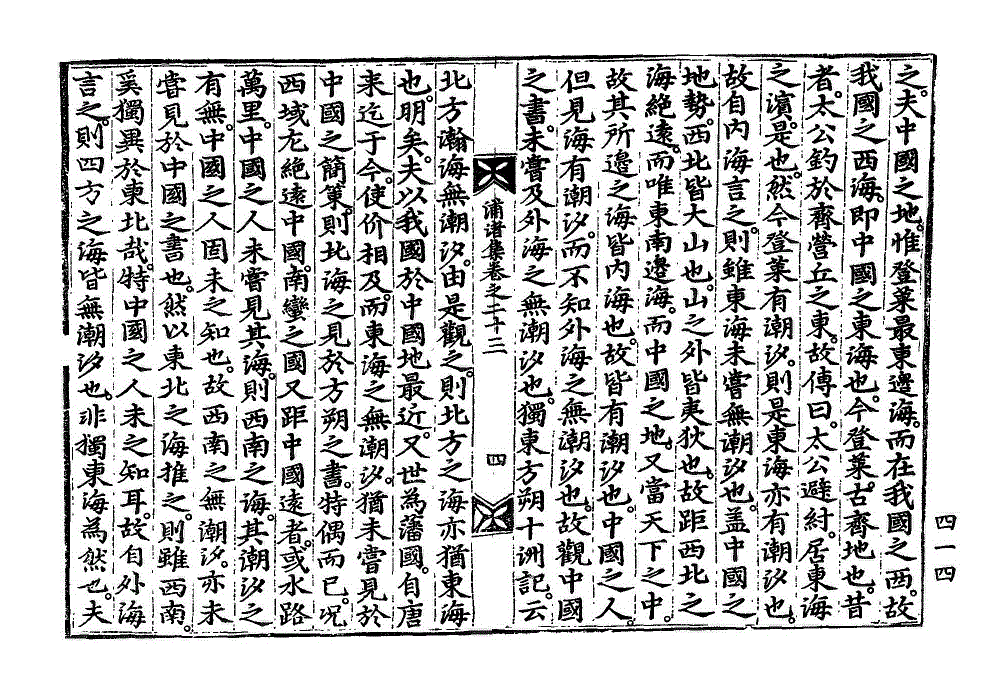 之。夫中国之地。惟登莱最东边海。而在我国之西。故我国之西海。即中国之东海也。今登莱。古齐地也。昔者。太公钓于齐营丘之东。故传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是也。然今登莱有潮汐。则是东海亦有潮汐也。故自内海言之。则虽东海未尝无潮汐也。盖中国之地势。西北皆大山也。山之外皆夷狄也。故距西北之海绝远。而唯东南边海。而中国之地。又当天下之中。故其所边之海皆内海也。故皆有潮汐也。中国之人。但见海有潮汐。而不知外海之无潮汐也。故观中国之书。未尝及外海之无潮汐也。独东方朔十洲记。云北方瀚海无潮汐。由是观之。则北方之海亦犹东海也。明矣。夫以我国于中国地最近。又世为藩国。自唐来迄于今。使价相及。而东海之无潮汐。犹未尝见于中国之简策。则北海之见于方朔之书。特偶而已。况西域尤绝远中国。南蛮之国又距中国远者。或水路万里。中国之人未尝见其海。则西南之海。其潮汐之有无。中国之人固未之知也。故西南之无潮汐。亦未尝见于中国之书也。然以东北之海推之。则虽西南。奚独异于东北哉。特中国之人未之知耳。故自外海言之。则四方之海皆无潮汐也。非独东海为然也。夫
之。夫中国之地。惟登莱最东边海。而在我国之西。故我国之西海。即中国之东海也。今登莱。古齐地也。昔者。太公钓于齐营丘之东。故传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是也。然今登莱有潮汐。则是东海亦有潮汐也。故自内海言之。则虽东海未尝无潮汐也。盖中国之地势。西北皆大山也。山之外皆夷狄也。故距西北之海绝远。而唯东南边海。而中国之地。又当天下之中。故其所边之海皆内海也。故皆有潮汐也。中国之人。但见海有潮汐。而不知外海之无潮汐也。故观中国之书。未尝及外海之无潮汐也。独东方朔十洲记。云北方瀚海无潮汐。由是观之。则北方之海亦犹东海也。明矣。夫以我国于中国地最近。又世为藩国。自唐来迄于今。使价相及。而东海之无潮汐。犹未尝见于中国之简策。则北海之见于方朔之书。特偶而已。况西域尤绝远中国。南蛮之国又距中国远者。或水路万里。中国之人未尝见其海。则西南之海。其潮汐之有无。中国之人固未之知也。故西南之无潮汐。亦未尝见于中国之书也。然以东北之海推之。则虽西南。奚独异于东北哉。特中国之人未之知耳。故自外海言之。则四方之海皆无潮汐也。非独东海为然也。夫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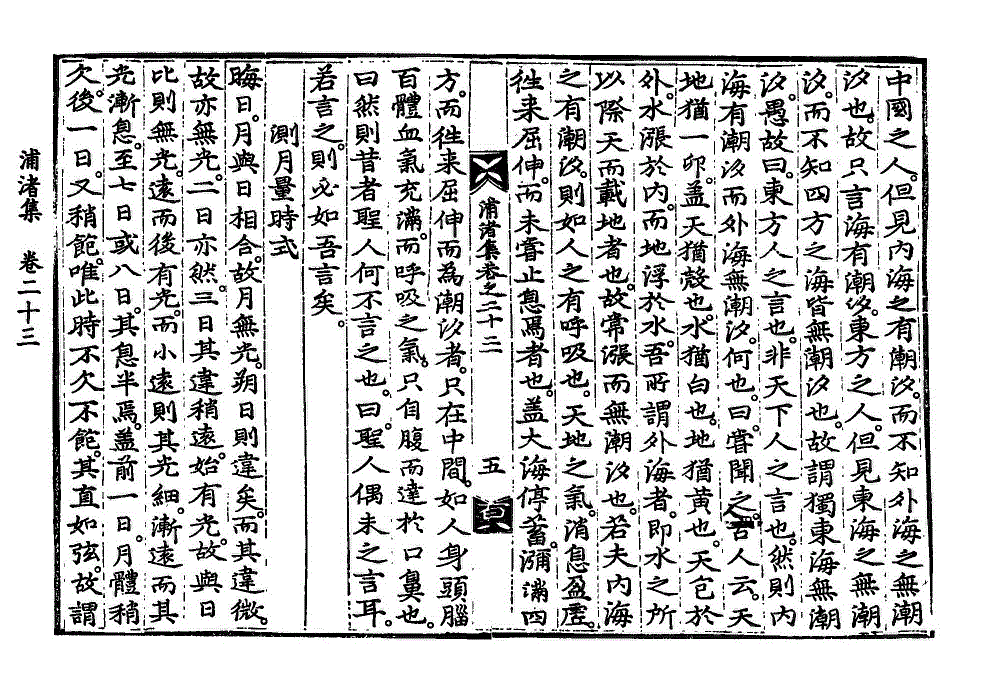 中国之人。但见内海之有潮汐。而不知外海之无潮汐也。故只言海有潮汐。东方之人。但见东海之无潮汐。而不知四方之海皆无潮汐也。故谓独东海无潮汐。愚故曰。东方人之言也。非天下人之言也。然则内海有潮汐而外海无潮汐。何也。曰。尝闻之。古人云。天地犹一卵。盖天犹壳也。水犹白也。地犹黄也。天包于外。水涨于内。而地浮于水。吾所谓外海者。即水之所以际天而载地者也。故常涨而无潮汐也。若夫内海之有潮汐。则如人之有呼吸也。天地之气。消息盈虚。往来屈伸。而未尝止息焉者也。盖大海停蓄。㳽满四方。而往来屈伸而为潮汐者。只在中间。如人身头脑百体血气充满。而呼吸之气。只自腹而达于口鼻也。曰然则昔者圣人何不言之也。曰。圣人偶未之言耳。若言之。则必如吾言矣。
中国之人。但见内海之有潮汐。而不知外海之无潮汐也。故只言海有潮汐。东方之人。但见东海之无潮汐。而不知四方之海皆无潮汐也。故谓独东海无潮汐。愚故曰。东方人之言也。非天下人之言也。然则内海有潮汐而外海无潮汐。何也。曰。尝闻之。古人云。天地犹一卵。盖天犹壳也。水犹白也。地犹黄也。天包于外。水涨于内。而地浮于水。吾所谓外海者。即水之所以际天而载地者也。故常涨而无潮汐也。若夫内海之有潮汐。则如人之有呼吸也。天地之气。消息盈虚。往来屈伸。而未尝止息焉者也。盖大海停蓄。㳽满四方。而往来屈伸而为潮汐者。只在中间。如人身头脑百体血气充满。而呼吸之气。只自腹而达于口鼻也。曰然则昔者圣人何不言之也。曰。圣人偶未之言耳。若言之。则必如吾言矣。测月量时式
晦日。月与日相合。故月无光。朔日则违矣。而其违微。故亦无光。二日亦然。三日其违稍远。始有光。故与日比则无光。远而后有光。而小远则其光细。渐远而其光渐息。至七日或八日。其息半焉。盖前一日。月体稍欠。后一日。又稍饱。唯此时不欠不饱。其直如弦。故谓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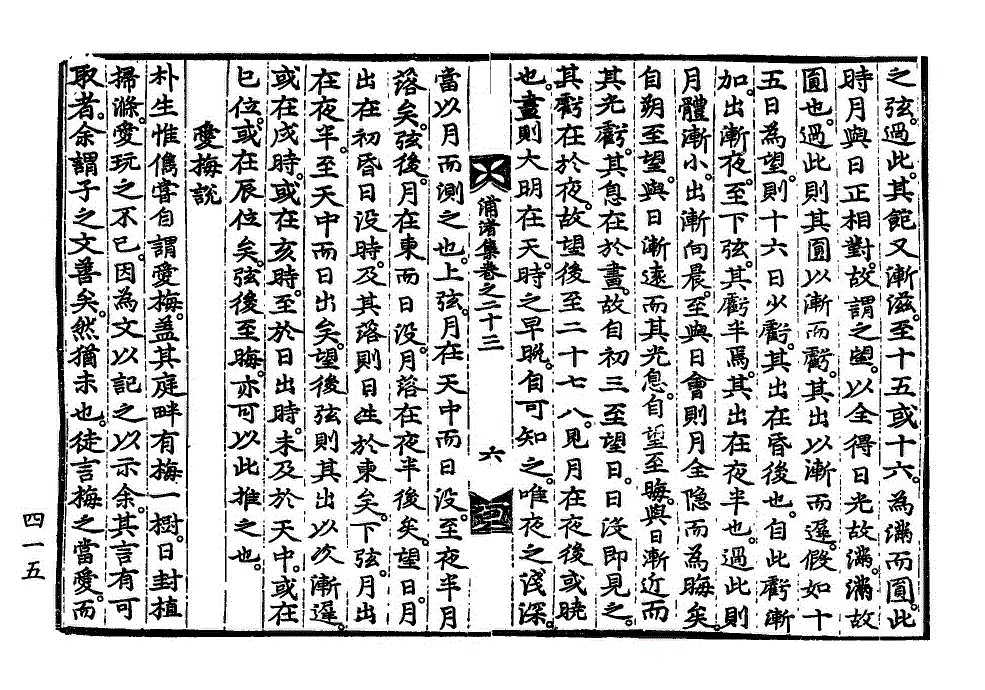 之弦。过此。其饱又渐滋。至十五或十六。为满而圆。此时月与日正相对。故谓之望。以全得日光故满。满故圆也。过此则其圆以渐而亏。其出以渐而迟。假如十五日为望。则十六日少亏。其出在昏后也。自此亏渐加。出渐夜。至下弦。其亏半焉。其出在夜半也。过此则月体渐小。出渐向晨。至与日会则月全隐而为晦矣。自朔至望。与日渐远而其光息。自望至晦。与日渐近而其光亏。其息在于昼。故自初三至望日。日没即见之。其亏在于夜。故望后至二十七八。见月在夜后或晓也。昼则大明在天。时之早晚。自可知之。唯夜之浅深。当以月而测之也。上弦。月在天中而日没。至夜半月落矣。弦后。月在东而日没。月落在夜半后矣。望日。月出在初昏日没时。及其落则日生于东矣。下弦。月出在夜半。至天中而日出矣。望后弦则其出以次渐迟。或在戌时。或在亥时。至于日出时。未及于天中。或在巳位。或在辰位矣。弦后至晦。亦可以此推之也。
之弦。过此。其饱又渐滋。至十五或十六。为满而圆。此时月与日正相对。故谓之望。以全得日光故满。满故圆也。过此则其圆以渐而亏。其出以渐而迟。假如十五日为望。则十六日少亏。其出在昏后也。自此亏渐加。出渐夜。至下弦。其亏半焉。其出在夜半也。过此则月体渐小。出渐向晨。至与日会则月全隐而为晦矣。自朔至望。与日渐远而其光息。自望至晦。与日渐近而其光亏。其息在于昼。故自初三至望日。日没即见之。其亏在于夜。故望后至二十七八。见月在夜后或晓也。昼则大明在天。时之早晚。自可知之。唯夜之浅深。当以月而测之也。上弦。月在天中而日没。至夜半月落矣。弦后。月在东而日没。月落在夜半后矣。望日。月出在初昏日没时。及其落则日生于东矣。下弦。月出在夜半。至天中而日出矣。望后弦则其出以次渐迟。或在戌时。或在亥时。至于日出时。未及于天中。或在巳位。或在辰位矣。弦后至晦。亦可以此推之也。爱梅说
朴生惟俊尝自谓爱梅。盖其庭畔有梅一树。日封植扫涤。爱玩之不已。因为文以记之以示余。其言有可取者。余谓子之文善矣。然犹未也。徒言梅之当爱。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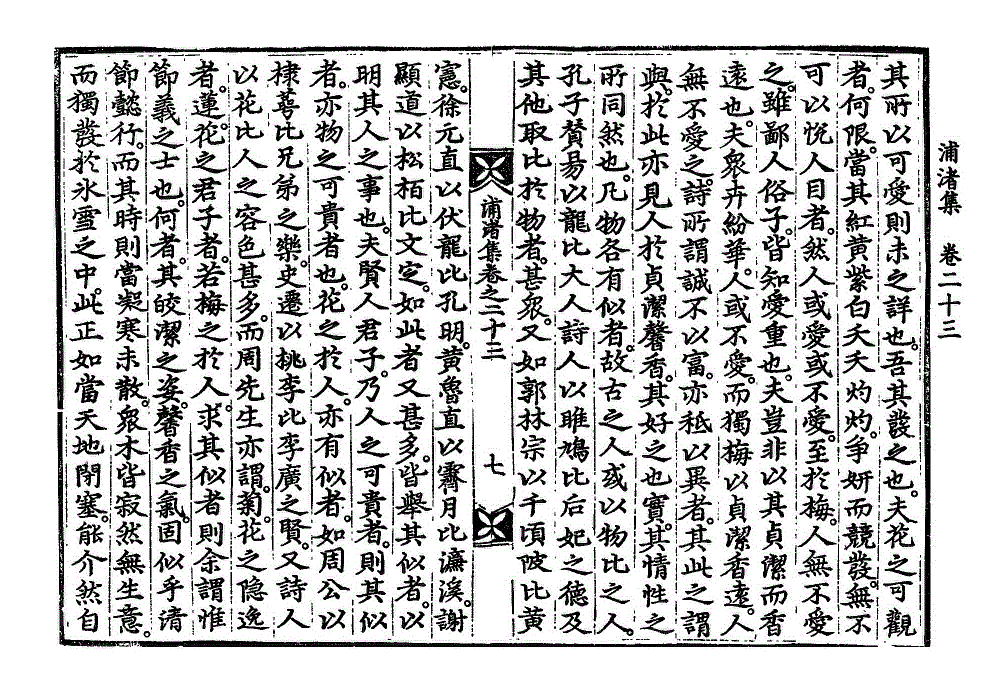 其所以可爱则未之详也。吾其发之也。夫花之可观者。何限。当其红黄紫白夭夭灼灼。争妍而竞发。无不可以悦人目者。然人或爱或不爱。至于梅。人无不爱之。虽鄙人俗子。皆知爱重也。夫岂非以其贞洁而香远也。夫众卉纷华。人或不爱。而独梅以贞洁香远。人无不爱之。诗所谓诚不以富。亦秪以异者。其此之谓与。于此亦见人于贞洁馨香。其好之也实。其情性之所同然也。凡物各有似者。故古之人或以物比之人。孔子赞易以龙比大人诗人以雎鸠比后妃之德及其他取比于物者。甚众。又如郭林宗以千顷陂比黄宪。徐元直以伏龙比孔明。黄鲁直以霁月比濂溪。谢显道以松柏比文定。如此者又甚多。皆举其似者。以明其人之事也。夫贤人君子。乃人之可贵者。则其似者。亦物之可贵者也。花之于人。亦有似者。如周公以棣萼比兄弟之乐。史迁以桃李比李广之贤。又诗人以花比人之容色甚多。而周先生亦谓。菊。花之隐逸者。莲。花之君子者。若梅之于人。求其似者则余谓惟节义之士也。何者。其皎洁之姿。馨香之气。固似乎清节懿行。而其时则当凝寒未散。众木皆寂然无生意。而独发于冰雪之中。此正如当天地闭塞。能介然自
其所以可爱则未之详也。吾其发之也。夫花之可观者。何限。当其红黄紫白夭夭灼灼。争妍而竞发。无不可以悦人目者。然人或爱或不爱。至于梅。人无不爱之。虽鄙人俗子。皆知爱重也。夫岂非以其贞洁而香远也。夫众卉纷华。人或不爱。而独梅以贞洁香远。人无不爱之。诗所谓诚不以富。亦秪以异者。其此之谓与。于此亦见人于贞洁馨香。其好之也实。其情性之所同然也。凡物各有似者。故古之人或以物比之人。孔子赞易以龙比大人诗人以雎鸠比后妃之德及其他取比于物者。甚众。又如郭林宗以千顷陂比黄宪。徐元直以伏龙比孔明。黄鲁直以霁月比濂溪。谢显道以松柏比文定。如此者又甚多。皆举其似者。以明其人之事也。夫贤人君子。乃人之可贵者。则其似者。亦物之可贵者也。花之于人。亦有似者。如周公以棣萼比兄弟之乐。史迁以桃李比李广之贤。又诗人以花比人之容色甚多。而周先生亦谓。菊。花之隐逸者。莲。花之君子者。若梅之于人。求其似者则余谓惟节义之士也。何者。其皎洁之姿。馨香之气。固似乎清节懿行。而其时则当凝寒未散。众木皆寂然无生意。而独发于冰雪之中。此正如当天地闭塞。能介然自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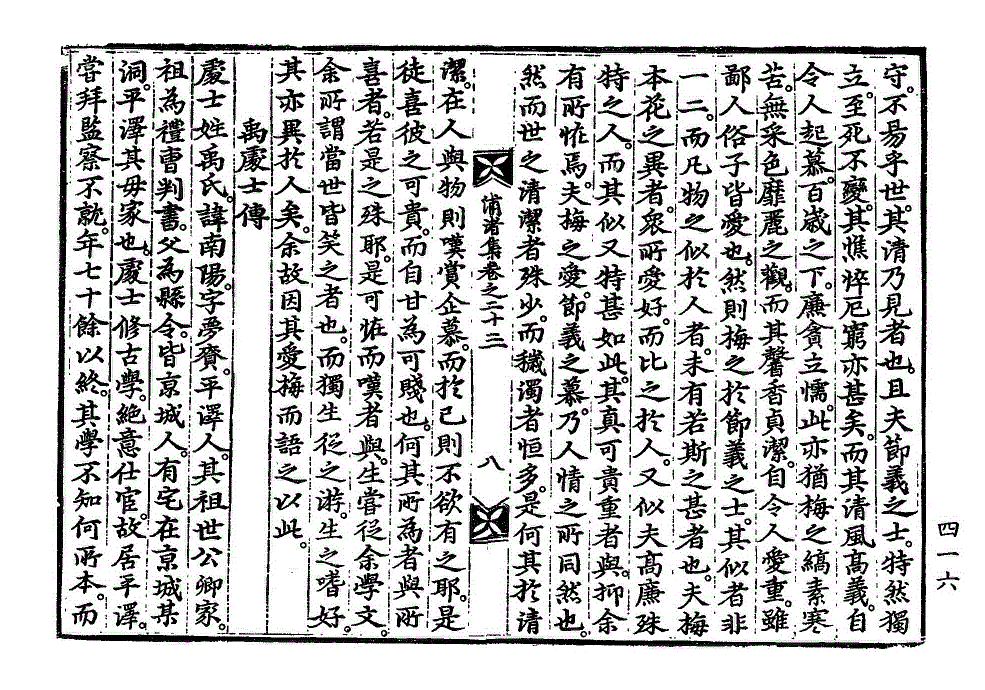 守。不易乎世。其清乃见者也。且夫节义之士。特然独立。至死不变。其憔悴厄穷亦甚矣。而其清风高义。自令人起慕。百岁之下。廉贪立懦。此亦犹梅之缟素寒苦。无采色靡丽之观。而其馨香贞洁。自令人爱重。虽鄙人俗子皆爱也。然则梅之于节义之士。其似者非一二。而凡物之似于人者。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梅本花之异者。众所爱好。而比之于人。又似夫高廉殊特之人。而其似又特甚如此。其真可贵重者与。抑余有所怪焉。夫梅之爱。节义之慕。乃人情之所同然也。然而世之清洁者殊少。而秽浊者恒多。是何其于清洁。在人与物则叹赏企慕。而于己则不欲有之耶。是徒喜彼之可贵。而自甘为可贱也。何其所为者与所喜者。若是之殊耶。是可怪而叹者与。生尝从余学文。余所谓当世皆笑之者也。而独生从之游。生之嗜好。其亦异于人矣。余故因其爱梅而语之以此。
守。不易乎世。其清乃见者也。且夫节义之士。特然独立。至死不变。其憔悴厄穷亦甚矣。而其清风高义。自令人起慕。百岁之下。廉贪立懦。此亦犹梅之缟素寒苦。无采色靡丽之观。而其馨香贞洁。自令人爱重。虽鄙人俗子皆爱也。然则梅之于节义之士。其似者非一二。而凡物之似于人者。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梅本花之异者。众所爱好。而比之于人。又似夫高廉殊特之人。而其似又特甚如此。其真可贵重者与。抑余有所怪焉。夫梅之爱。节义之慕。乃人情之所同然也。然而世之清洁者殊少。而秽浊者恒多。是何其于清洁。在人与物则叹赏企慕。而于己则不欲有之耶。是徒喜彼之可贵。而自甘为可贱也。何其所为者与所喜者。若是之殊耶。是可怪而叹者与。生尝从余学文。余所谓当世皆笑之者也。而独生从之游。生之嗜好。其亦异于人矣。余故因其爱梅而语之以此。禹处士传
处士姓禹氏。讳南阳。字梦赉。平泽人。其祖世公卿家。祖为礼曹判书。父为县令。皆京城人。有宅在京城某洞。平泽其母家也。处士修古学。绝意仕宦。故居平泽。尝拜监察不就。年七十馀以终。其学不知何所本。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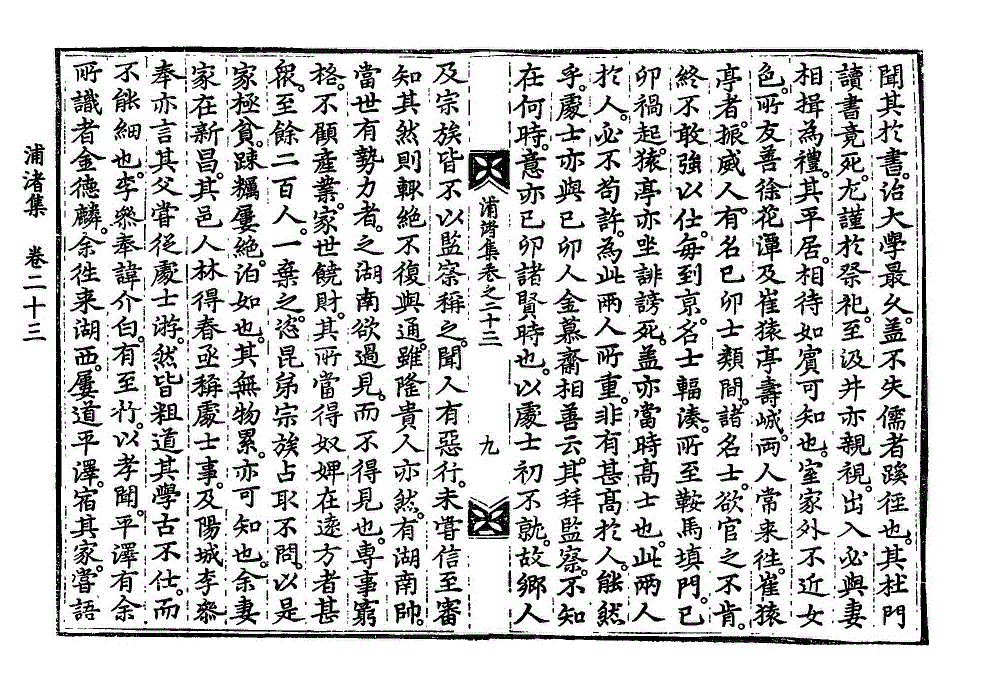 闻其于书。治大学最久。盖不失儒者蹊径也。其杜门读书竟死。尤谨于祭祀。至汲井亦亲视。出入必与妻相揖为礼。其平居。相待如宾可知也。室家外不近女色。所友善徐花潭及崔猿亭寿峸。两人常来往。崔猿亭者。振威人。有名己卯士类间。诸名士。欲官之不肯。终不敢强以仕。每到京。名士辐凑。所至鞍马填门。己卯祸起。猿亭亦坐诽谤死。盖亦当时高士也。此两人于人。必不苟许。为此两人所重。非有甚高于人。能然乎。处士亦与己卯人金慕斋相善云。其拜监察。不知在何时。意亦己卯诸贤时也。以处士初不就。故乡人及宗族皆不以监察称之。闻人有恶行。未尝信至审知其然则辄绝不复与通。虽隆贵人亦然。有湖南帅。当世有势力者。之湖南欲过见。而不得见也。专事穷格。不顾产业。家世饶财。其所当得奴婢在远方者甚众。至馀二百人。一弃之。恣昆弟宗族占取不问。以是家极贫。疏粝屡绝。泊如也。其无物累。亦可知也。余妻家在新昌。其邑人林得春亟称处士事。及阳城李参奉亦言其父尝从处士游。然皆粗道其学古不仕。而不能细也。李参奉讳介白。有至行。以孝闻。平泽有余所识者金德麟。余往来湖西。屡道平泽。宿其家。尝语
闻其于书。治大学最久。盖不失儒者蹊径也。其杜门读书竟死。尤谨于祭祀。至汲井亦亲视。出入必与妻相揖为礼。其平居。相待如宾可知也。室家外不近女色。所友善徐花潭及崔猿亭寿峸。两人常来往。崔猿亭者。振威人。有名己卯士类间。诸名士。欲官之不肯。终不敢强以仕。每到京。名士辐凑。所至鞍马填门。己卯祸起。猿亭亦坐诽谤死。盖亦当时高士也。此两人于人。必不苟许。为此两人所重。非有甚高于人。能然乎。处士亦与己卯人金慕斋相善云。其拜监察。不知在何时。意亦己卯诸贤时也。以处士初不就。故乡人及宗族皆不以监察称之。闻人有恶行。未尝信至审知其然则辄绝不复与通。虽隆贵人亦然。有湖南帅。当世有势力者。之湖南欲过见。而不得见也。专事穷格。不顾产业。家世饶财。其所当得奴婢在远方者甚众。至馀二百人。一弃之。恣昆弟宗族占取不问。以是家极贫。疏粝屡绝。泊如也。其无物累。亦可知也。余妻家在新昌。其邑人林得春亟称处士事。及阳城李参奉亦言其父尝从处士游。然皆粗道其学古不仕。而不能细也。李参奉讳介白。有至行。以孝闻。平泽有余所识者金德麟。余往来湖西。屡道平泽。宿其家。尝语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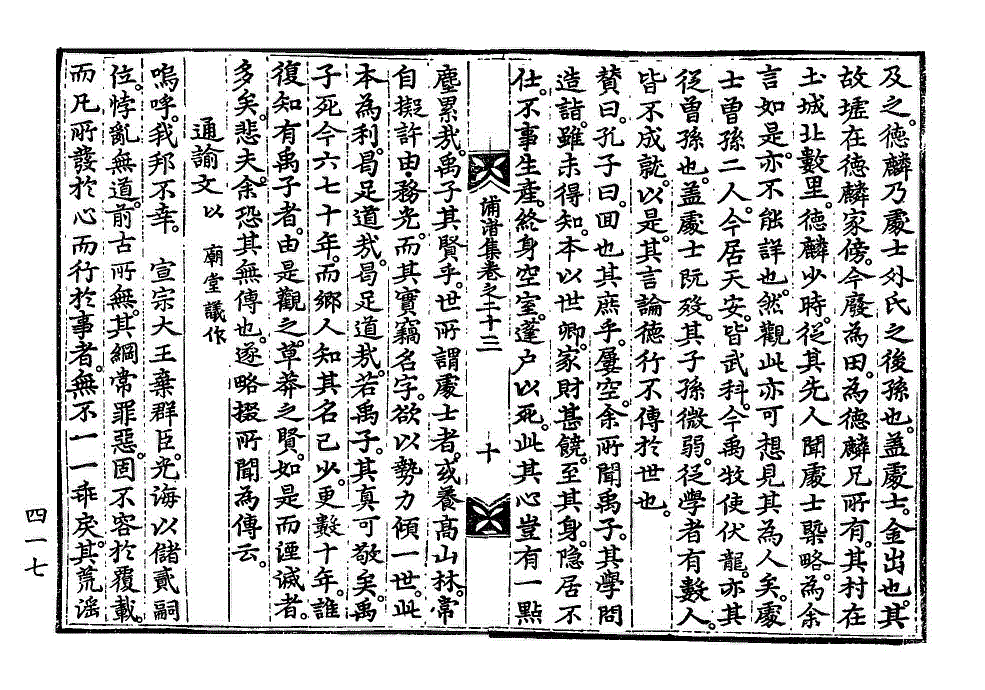 及之。德麟乃处士外氏之后孙也。盖处士。金出也。其故墟在德麟家傍。今废为田。为德麟兄所有。其村在土城北数里。德麟少时。从其先人闻处士槩略。为余言如是。亦不能详也。然观此亦可想见其为人矣。处士曾孙二人。今居天安。皆武科。今禹牧使伏龙。亦其从曾孙也。盖处士既殁。其子孙微弱。从学者有数人。皆不成就。以是。其言论德行不传于世也。
及之。德麟乃处士外氏之后孙也。盖处士。金出也。其故墟在德麟家傍。今废为田。为德麟兄所有。其村在土城北数里。德麟少时。从其先人闻处士槩略。为余言如是。亦不能详也。然观此亦可想见其为人矣。处士曾孙二人。今居天安。皆武科。今禹牧使伏龙。亦其从曾孙也。盖处士既殁。其子孙微弱。从学者有数人。皆不成就。以是。其言论德行不传于世也。赞曰。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余所闻禹子。其学问造诣。虽未得知。本以世卿。家财甚饶。至其身。隐居不仕。不事生产。终身空室。蓬户以死。此其心岂有一点尘累哉。禹子其贤乎。世所谓处士者。或养高山林。常自拟许由,务光。而其实窃名字。欲以势力倾一世。此本为利。曷足道哉。曷足道哉。若禹子。其真可敬矣。禹子死今六七十年。而乡人知其名已少。更数十年。谁复知有禹子者。由是观之。草莽之贤。如是而湮灭者。多矣。悲夫。余恐其无传也。遂略掇所闻为传云。
通谕文(以 庙堂议作)
呜呼。我邦不幸。 宣宗大王弃群臣。光海以储贰嗣位。悖乱无道。前古所无。其纲常罪恶。固不容于覆载。而凡所发于心而行于事者。无不一一乖戾。其荒淫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8H 页
 之乐。货贿之集。刑罚之淫。土木之繁。聚敛之暴。惟日不足。靡所不至。人伦既灭。民生困极。 宗社危如累卵矣。幸而天未绝晋。眷佑我 殿下。纠合义旅。遂行诛讨。奉迎 慈殿于幽囚之中。复正位号。事之尽孝。其助桀为恶之辈。诛夷窜逐。各以轻重论罪。以泄神人之愤。凡国中所谓善人君子素有名闻为群凶所斥逐及退遁山野者。悉皆召还。咸集 朝廷。凡光海时暴政苛敛。一皆停罢。人伦复正。 朝廷复清。生民得出于汤火。 宗社将绝而再安。此我 殿下所以大有功于伦纪。大有功于 宗社。大有功于民生。诚天下之大义。万世之大功。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奈何 反正以来。逆变相继。前年七月。逆贼柳湔等结约之书。被告名在书中者几四十人。奇自献其首也。而其中柳梦寅亡逃被捉。榜掠不多。一一自服其所为谋。至供其所为诗。言欲为废主复雠。至于八月。李德男告金德元,朱大允等。皆一一招服。十月。黄晛,李有林等设谋发觉。穷问取服。颇得其党与鞫治。又有凶檄遍投都监将官家。其言极凶。今年正月。文晦,李佑探知逆谋以告。奇自献,全有亨等已就狱。而
之乐。货贿之集。刑罚之淫。土木之繁。聚敛之暴。惟日不足。靡所不至。人伦既灭。民生困极。 宗社危如累卵矣。幸而天未绝晋。眷佑我 殿下。纠合义旅。遂行诛讨。奉迎 慈殿于幽囚之中。复正位号。事之尽孝。其助桀为恶之辈。诛夷窜逐。各以轻重论罪。以泄神人之愤。凡国中所谓善人君子素有名闻为群凶所斥逐及退遁山野者。悉皆召还。咸集 朝廷。凡光海时暴政苛敛。一皆停罢。人伦复正。 朝廷复清。生民得出于汤火。 宗社将绝而再安。此我 殿下所以大有功于伦纪。大有功于 宗社。大有功于民生。诚天下之大义。万世之大功。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奈何 反正以来。逆变相继。前年七月。逆贼柳湔等结约之书。被告名在书中者几四十人。奇自献其首也。而其中柳梦寅亡逃被捉。榜掠不多。一一自服其所为谋。至供其所为诗。言欲为废主复雠。至于八月。李德男告金德元,朱大允等。皆一一招服。十月。黄晛,李有林等设谋发觉。穷问取服。颇得其党与鞫治。又有凶檄遍投都监将官家。其言极凶。今年正月。文晦,李佑探知逆谋以告。奇自献,全有亨等已就狱。而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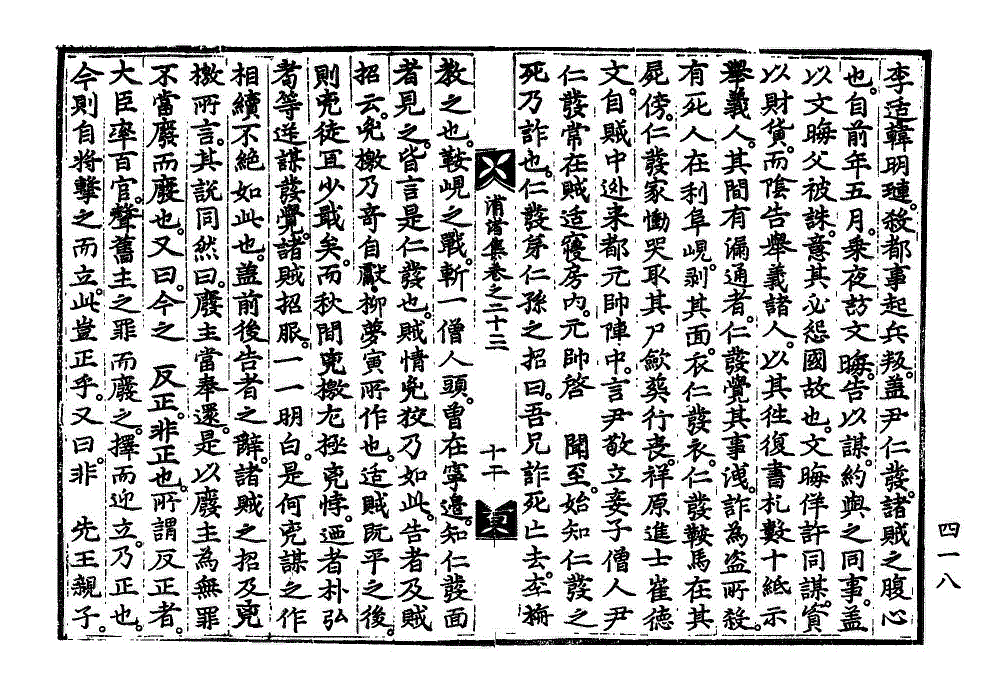 李适,韩明琏。杀都事起兵叛。盖尹仁发。诸贼之腹心也。自前年五月。乘夜访文晦。告以谋。约与之同事。盖以文晦父被诛。意其必怨国故也。文晦佯许同谋。资以财货。而阴告举义诸人。以其往复书札数十纸示举义人。其间有漏通者。仁发觉其事泄。诈为盗所杀。有死人在利阜岘。剥其面。衣仁发衣。仁发鞍马在其尸傍。仁发家恸哭取其尸敛葬行丧。祥原进士崔德文。自贼中逃来都元帅阵中。言尹敬立妾子僧人尹仁发常在贼适寝房内。元帅启 闻至。始知仁发之死乃诈也。仁发弟仁孙之招曰。吾兄诈死亡去。李栴教之也。鞍岘之战。斩一僧人头。曾在宁边。知仁发面者见之。皆言是仁发也。贼情凶狡乃如此。告者及贼招云。凶檄乃奇自献,柳梦寅所作也。适贼既平之后。则凶徒宜少戢矣。而秋间凶檄尤极凶悖。乃者朴弘耇等逆谋发觉。诸贼招服。一一明白。是何凶谋之作相续不绝如此也。盖前后告者之辞。诸贼之招及凶檄所言。其说同然曰。废主当奉还。是以废主为无罪不当废而废也。又曰。今之 反正。非正也。所谓反正者。大臣率百官。声旧主之罪而废之。择而迎立。乃正也。今则自将击之而立。此岂正乎。又曰。非 先王亲子。
李适,韩明琏。杀都事起兵叛。盖尹仁发。诸贼之腹心也。自前年五月。乘夜访文晦。告以谋。约与之同事。盖以文晦父被诛。意其必怨国故也。文晦佯许同谋。资以财货。而阴告举义诸人。以其往复书札数十纸示举义人。其间有漏通者。仁发觉其事泄。诈为盗所杀。有死人在利阜岘。剥其面。衣仁发衣。仁发鞍马在其尸傍。仁发家恸哭取其尸敛葬行丧。祥原进士崔德文。自贼中逃来都元帅阵中。言尹敬立妾子僧人尹仁发常在贼适寝房内。元帅启 闻至。始知仁发之死乃诈也。仁发弟仁孙之招曰。吾兄诈死亡去。李栴教之也。鞍岘之战。斩一僧人头。曾在宁边。知仁发面者见之。皆言是仁发也。贼情凶狡乃如此。告者及贼招云。凶檄乃奇自献,柳梦寅所作也。适贼既平之后。则凶徒宜少戢矣。而秋间凶檄尤极凶悖。乃者朴弘耇等逆谋发觉。诸贼招服。一一明白。是何凶谋之作相续不绝如此也。盖前后告者之辞。诸贼之招及凶檄所言。其说同然曰。废主当奉还。是以废主为无罪不当废而废也。又曰。今之 反正。非正也。所谓反正者。大臣率百官。声旧主之罪而废之。择而迎立。乃正也。今则自将击之而立。此岂正乎。又曰。非 先王亲子。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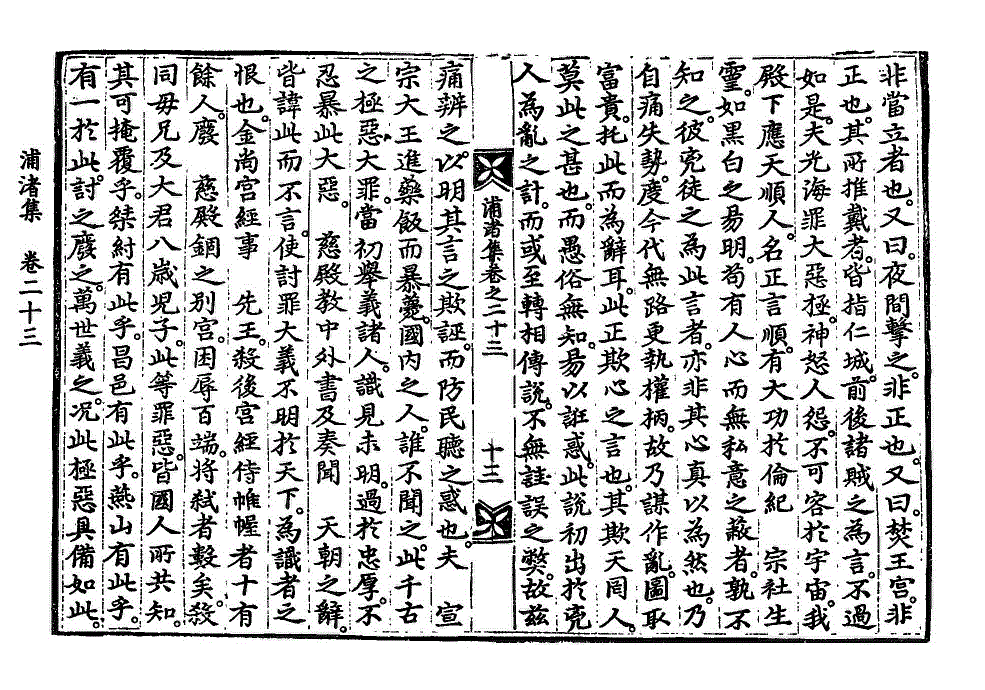 非当立者也。又曰。夜间击之。非正也。又曰。焚王宫。非正也。其所推戴者。皆指仁城。前后诸贼之为言。不过如是。夫光海罪大恶极。神怒人怨。不可容于宇宙。我殿下应天顺人。名正言顺。有大功于伦纪 宗社生灵。如黑白之易明。苟有人心而无私意之蔽者。孰不知之。彼凶徒之为此言者。亦非其心真以为然也。乃自痛失势。度今代无路更执权柄。故乃谋作乱。图取富贵。托此而为辞耳。此正欺心之言也。其欺天罔人。莫此之甚也。而愚俗无知。易以诳惑。此说初出于凶人为乱之计。而或至转相传说。不无诖误之弊。故玆痛辨之。以明其言之欺诬。而防民听之惑也。夫 宣宗大王进药饭而暴薨。国内之人。谁不闻之。此千古之极恶大罪。当初举义诸人。识见未明。过于忠厚。不忍暴此大恶。 慈殿教中外书及奏闻 天朝之辞。皆讳此而不言。使讨罪大义不明于天下。为识者之恨也。金尚宫经事 先王。杀后宫经侍帷幄者十有馀人。废 慈殿锢之别宫。困辱百端。将弑者数矣。杀同母兄及大君八岁儿子。此等罪恶。皆国人所共知。其可掩覆乎。桀纣有此乎。昌邑有此乎。燕山有此乎。有一于此。讨之废之。万世义之。况此极恶具备如此。
非当立者也。又曰。夜间击之。非正也。又曰。焚王宫。非正也。其所推戴者。皆指仁城。前后诸贼之为言。不过如是。夫光海罪大恶极。神怒人怨。不可容于宇宙。我殿下应天顺人。名正言顺。有大功于伦纪 宗社生灵。如黑白之易明。苟有人心而无私意之蔽者。孰不知之。彼凶徒之为此言者。亦非其心真以为然也。乃自痛失势。度今代无路更执权柄。故乃谋作乱。图取富贵。托此而为辞耳。此正欺心之言也。其欺天罔人。莫此之甚也。而愚俗无知。易以诳惑。此说初出于凶人为乱之计。而或至转相传说。不无诖误之弊。故玆痛辨之。以明其言之欺诬。而防民听之惑也。夫 宣宗大王进药饭而暴薨。国内之人。谁不闻之。此千古之极恶大罪。当初举义诸人。识见未明。过于忠厚。不忍暴此大恶。 慈殿教中外书及奏闻 天朝之辞。皆讳此而不言。使讨罪大义不明于天下。为识者之恨也。金尚宫经事 先王。杀后宫经侍帷幄者十有馀人。废 慈殿锢之别宫。困辱百端。将弑者数矣。杀同母兄及大君八岁儿子。此等罪恶。皆国人所共知。其可掩覆乎。桀纣有此乎。昌邑有此乎。燕山有此乎。有一于此。讨之废之。万世义之。况此极恶具备如此。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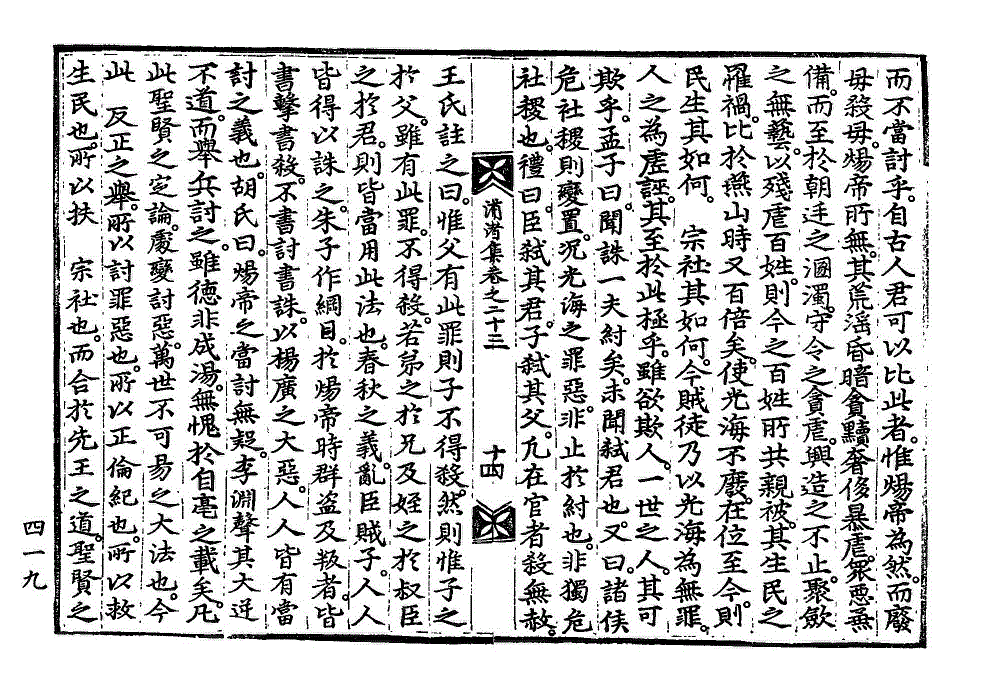 而不当讨乎。自古人君可以比此者。惟炀帝为然。而废母杀母。炀帝所无。其荒淫昏暗贪黩奢侈暴虐。众恶兼备。而至于朝廷之溷浊。守令之贪虐。兴造之不止。聚敛之无艺。以残虐百姓。则今之百姓所共亲被。其生民之罹祸。比于燕山时又百倍矣。使光海不废。在位至今。则民生其如何。 宗社其如何。今贼徒乃以光海为无罪。人之为虚诬。其至于此极乎。虽欲欺人。一世之人。其可欺乎。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况光海之罪恶。非止于纣也。非独危社稷也。礼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杀无赦。王氏注之曰。惟父有此罪则子不得杀。然则惟子之于父。虽有此罪。不得杀。若弟之于兄及侄之于叔臣之于君。则皆当用此法也。春秋之义。乱臣贼子。人人皆得以诛之。朱子作纲目。于炀帝时群盗及叛者。皆书击书杀。不书讨书诛。以杨广之大恶。人人皆有当讨之义也。胡氏曰。炀帝之当讨无疑。李渊声其大逆不道。而举兵讨之。虽德非成汤。无愧于自亳之载矣。凡此圣贤之定论。处变讨恶。万世不可易之大法也。今此 反正之举。所以讨罪恶也。所以正伦纪也。所以救生民也。所以扶 宗社也。而合于先王之道。圣贤之
而不当讨乎。自古人君可以比此者。惟炀帝为然。而废母杀母。炀帝所无。其荒淫昏暗贪黩奢侈暴虐。众恶兼备。而至于朝廷之溷浊。守令之贪虐。兴造之不止。聚敛之无艺。以残虐百姓。则今之百姓所共亲被。其生民之罹祸。比于燕山时又百倍矣。使光海不废。在位至今。则民生其如何。 宗社其如何。今贼徒乃以光海为无罪。人之为虚诬。其至于此极乎。虽欲欺人。一世之人。其可欺乎。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况光海之罪恶。非止于纣也。非独危社稷也。礼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杀无赦。王氏注之曰。惟父有此罪则子不得杀。然则惟子之于父。虽有此罪。不得杀。若弟之于兄及侄之于叔臣之于君。则皆当用此法也。春秋之义。乱臣贼子。人人皆得以诛之。朱子作纲目。于炀帝时群盗及叛者。皆书击书杀。不书讨书诛。以杨广之大恶。人人皆有当讨之义也。胡氏曰。炀帝之当讨无疑。李渊声其大逆不道。而举兵讨之。虽德非成汤。无愧于自亳之载矣。凡此圣贤之定论。处变讨恶。万世不可易之大法也。今此 反正之举。所以讨罪恶也。所以正伦纪也。所以救生民也。所以扶 宗社也。而合于先王之道。圣贤之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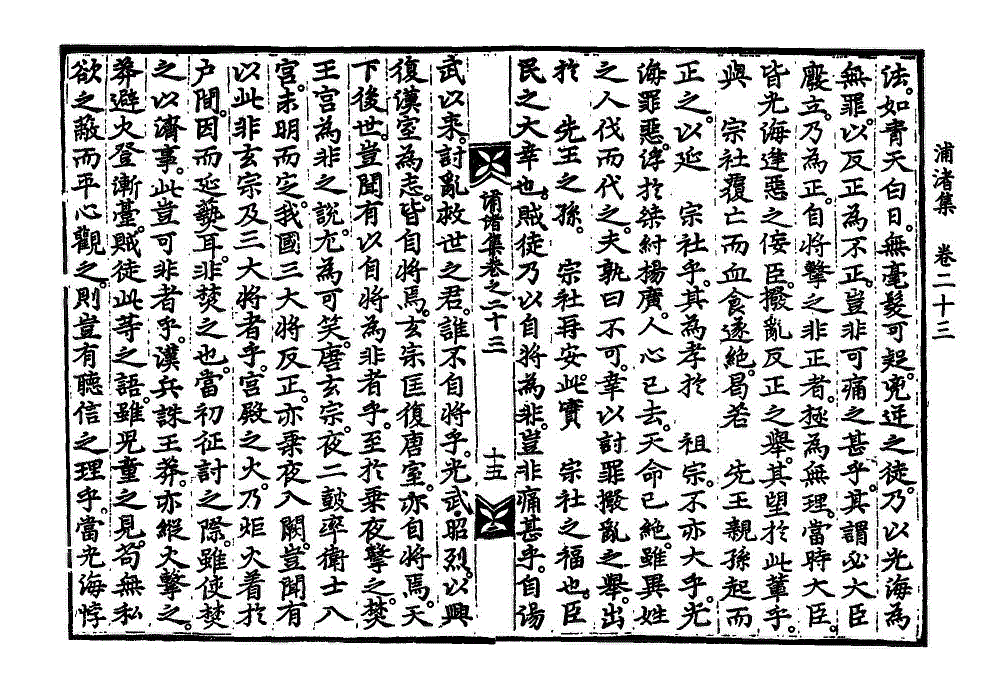 法。如青天白日。无毫发可疑。凶逆之徒。乃以光海为无罪。以反正为不正。岂非可痛之甚乎。其谓必大臣废立。乃为正。自将击之非正者。极为无理。当时大臣。皆光海逢恶之佞臣。拨乱反正之举。其望于此辈乎。与 宗社覆亡而血食遂绝。曷若 先王亲孙起而正之。以延 宗社乎。其为孝于 祖宗。不亦大乎。光海罪恶。浮于桀纣杨广。人心已去。天命已绝。虽异姓之人伐而代之。夫孰曰不可。幸以讨罪拨乱之举。出于 先王之孙。 宗社再安。此实 宗社之福也。臣民之大幸也。贼徒乃以自将为非。岂非痛甚乎。自汤武以来。讨乱救世之君。谁不自将乎。光武,昭烈。以兴复汉室为志。皆自将焉。玄宗匡复唐室。亦自将焉。天下后世。岂闻有以自将为非者乎。至于乘夜击之。焚王宫为非之说。尤为可笑。唐玄宗。夜二鼓率卫士入宫。未明而定。我国三大将反正。亦乘夜入阙。岂闻有以此非玄宗及三大将者乎。宫殿之火。乃炬火着于户间。因而延爇耳。非焚之也。当初征讨之际。虽使焚之以济事。此岂可非者乎。汉兵诛王莽。亦纵火击之。莽避火登渐台。贼徒此等之语。虽儿童之见。苟无私欲之蔽而平心观之。则岂有听信之理乎。当光海悖
法。如青天白日。无毫发可疑。凶逆之徒。乃以光海为无罪。以反正为不正。岂非可痛之甚乎。其谓必大臣废立。乃为正。自将击之非正者。极为无理。当时大臣。皆光海逢恶之佞臣。拨乱反正之举。其望于此辈乎。与 宗社覆亡而血食遂绝。曷若 先王亲孙起而正之。以延 宗社乎。其为孝于 祖宗。不亦大乎。光海罪恶。浮于桀纣杨广。人心已去。天命已绝。虽异姓之人伐而代之。夫孰曰不可。幸以讨罪拨乱之举。出于 先王之孙。 宗社再安。此实 宗社之福也。臣民之大幸也。贼徒乃以自将为非。岂非痛甚乎。自汤武以来。讨乱救世之君。谁不自将乎。光武,昭烈。以兴复汉室为志。皆自将焉。玄宗匡复唐室。亦自将焉。天下后世。岂闻有以自将为非者乎。至于乘夜击之。焚王宫为非之说。尤为可笑。唐玄宗。夜二鼓率卫士入宫。未明而定。我国三大将反正。亦乘夜入阙。岂闻有以此非玄宗及三大将者乎。宫殿之火。乃炬火着于户间。因而延爇耳。非焚之也。当初征讨之际。虽使焚之以济事。此岂可非者乎。汉兵诛王莽。亦纵火击之。莽避火登渐台。贼徒此等之语。虽儿童之见。苟无私欲之蔽而平心观之。则岂有听信之理乎。当光海悖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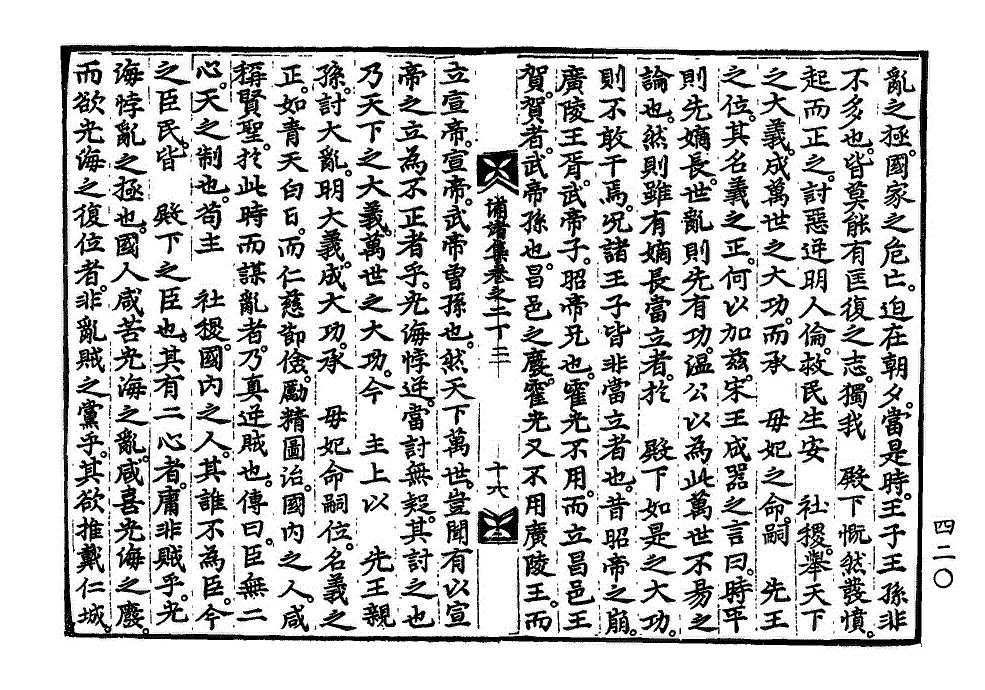 乱之极。国家之危亡。迫在朝夕。当是时。王子王孙非不多也。皆莫能有匡复之志。独我 殿下慨然发愤。起而正之。讨恶逆明人伦。救民生安 社稷。举天下之大义。成万世之大功。而承 母妃之命。嗣 先王之位。其名义之正。何以加玆。宋王成器之言曰。时平则先嫡长。世乱则先有功。温公以为此万世不易之论也。然则虽有嫡长当立者。于 殿下如是之大功。则不敢干焉。况诸王子皆非当立者也。昔昭帝之崩。广陵王胥。武帝子。昭帝兄也。霍光不用。而立昌邑王贺。贺者。武帝孙也。昌邑之废。霍光又不用广陵王。而立宣帝。宣帝。武帝曾孙也。然天下万世。岂闻有以宣帝之立为不正者乎。光海悖逆。当讨无疑。其讨之也乃天下之大义。万世之大功。今 主上以 先王亲孙。讨大乱。明大义。成大功。承 母妃命嗣位。名义之正。如青天白日。而仁慈节俭。励精图治。国内之人。咸称贤圣。于此时而谋乱者。乃真逆贼也。传曰。臣无二心。天之制也。苟主 社稷。国内之人(一作民)。其谁不为臣。今之臣民。皆 殿下之臣也。其有二心者。庸非贼乎。光海悖乱之极也。国人咸苦光海之乱。咸喜光海之废。而欲光海之复位者。非乱贼之党乎。其欲推戴仁城。
乱之极。国家之危亡。迫在朝夕。当是时。王子王孙非不多也。皆莫能有匡复之志。独我 殿下慨然发愤。起而正之。讨恶逆明人伦。救民生安 社稷。举天下之大义。成万世之大功。而承 母妃之命。嗣 先王之位。其名义之正。何以加玆。宋王成器之言曰。时平则先嫡长。世乱则先有功。温公以为此万世不易之论也。然则虽有嫡长当立者。于 殿下如是之大功。则不敢干焉。况诸王子皆非当立者也。昔昭帝之崩。广陵王胥。武帝子。昭帝兄也。霍光不用。而立昌邑王贺。贺者。武帝孙也。昌邑之废。霍光又不用广陵王。而立宣帝。宣帝。武帝曾孙也。然天下万世。岂闻有以宣帝之立为不正者乎。光海悖逆。当讨无疑。其讨之也乃天下之大义。万世之大功。今 主上以 先王亲孙。讨大乱。明大义。成大功。承 母妃命嗣位。名义之正。如青天白日。而仁慈节俭。励精图治。国内之人。咸称贤圣。于此时而谋乱者。乃真逆贼也。传曰。臣无二心。天之制也。苟主 社稷。国内之人(一作民)。其谁不为臣。今之臣民。皆 殿下之臣也。其有二心者。庸非贼乎。光海悖乱之极也。国人咸苦光海之乱。咸喜光海之废。而欲光海之复位者。非乱贼之党乎。其欲推戴仁城。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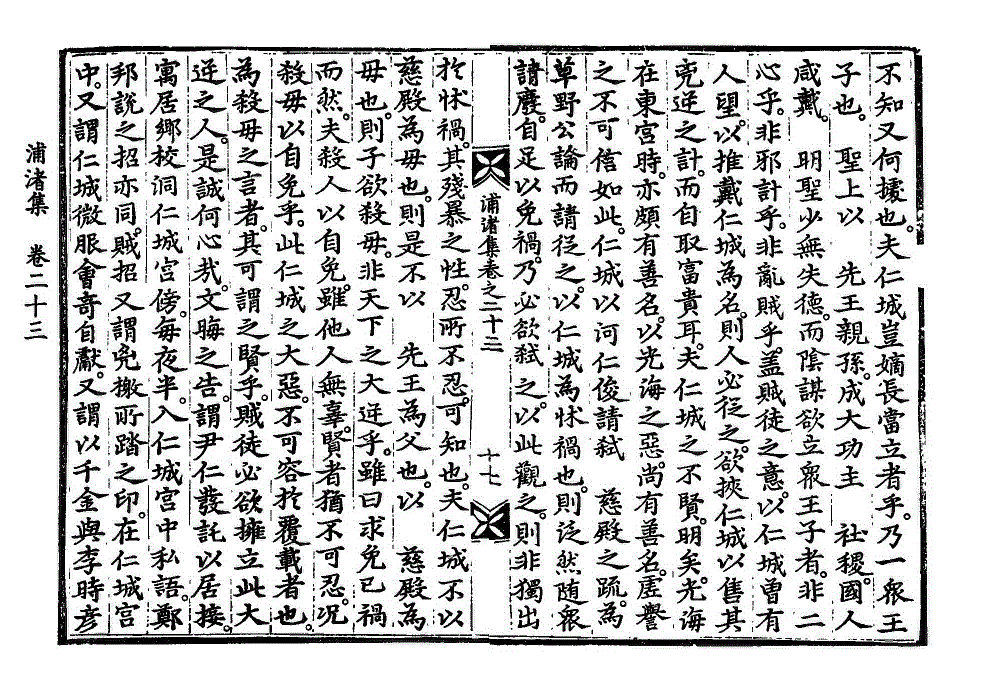 不知又何据也。夫仁城岂嫡长当立者乎。乃一众王子也。 圣上以 先王亲孙。成大功主 社稷。国人咸戴。 明圣少无失德。而阴谋欲立众王子者。非二心乎。非邪计乎。非乱贼乎。盖贼徒之意。以仁城曾有人望。以推戴仁城为名。则人必从之。欲挟仁城以售其凶逆之计。而自取富贵耳。夫仁城之不贤。明矣。光海在东宫时。亦颇有善名。以光海之恶。尚有善名。虚誉之不可信如此。仁城以河仁俊请弑 慈殿之疏。为草野公论而请从之。以仁城为怵祸也。则泛然随众请废。自足以免祸。乃必欲弑之。以此观之。则非独出于怵祸。其残暴之性。忍所不忍。可知也。夫仁城不以慈殿为母也。则是不以 先王为父也。以 慈殿为母也。则子欲杀母。非天下之大逆乎。虽曰求免己祸而然。夫杀人以自免。虽他人无辜。贤者犹不可忍。况杀母以自免乎。此仁城之大恶。不可容于覆载者也。为杀母之言者。其可谓之贤乎。贼徒必欲拥立此大逆之人。是诚何心哉。文晦之告。谓尹仁发托以居接。寓居乡校洞仁城宫傍。每夜半。入仁城宫中私语。郑邦说之招亦同。贼招又谓凶檄所踏之印。在仁城宫中。又谓仁城微服会奇自献。又谓以千金与李时彦
不知又何据也。夫仁城岂嫡长当立者乎。乃一众王子也。 圣上以 先王亲孙。成大功主 社稷。国人咸戴。 明圣少无失德。而阴谋欲立众王子者。非二心乎。非邪计乎。非乱贼乎。盖贼徒之意。以仁城曾有人望。以推戴仁城为名。则人必从之。欲挟仁城以售其凶逆之计。而自取富贵耳。夫仁城之不贤。明矣。光海在东宫时。亦颇有善名。以光海之恶。尚有善名。虚誉之不可信如此。仁城以河仁俊请弑 慈殿之疏。为草野公论而请从之。以仁城为怵祸也。则泛然随众请废。自足以免祸。乃必欲弑之。以此观之。则非独出于怵祸。其残暴之性。忍所不忍。可知也。夫仁城不以慈殿为母也。则是不以 先王为父也。以 慈殿为母也。则子欲杀母。非天下之大逆乎。虽曰求免己祸而然。夫杀人以自免。虽他人无辜。贤者犹不可忍。况杀母以自免乎。此仁城之大恶。不可容于覆载者也。为杀母之言者。其可谓之贤乎。贼徒必欲拥立此大逆之人。是诚何心哉。文晦之告。谓尹仁发托以居接。寓居乡校洞仁城宫傍。每夜半。入仁城宫中私语。郑邦说之招亦同。贼招又谓凶檄所踏之印。在仁城宫中。又谓仁城微服会奇自献。又谓以千金与李时彦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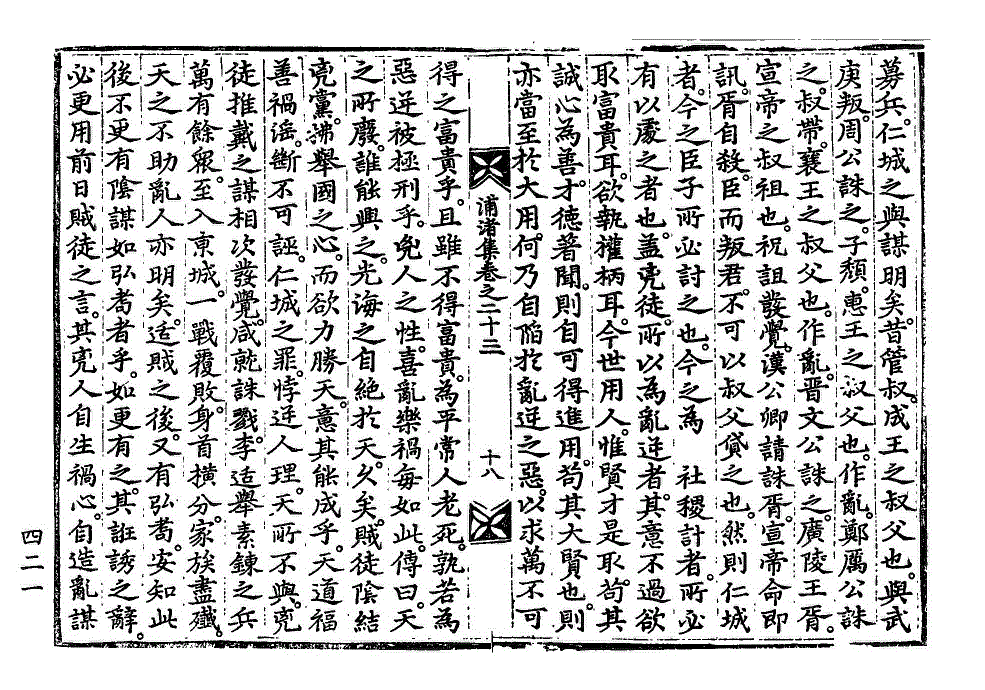 募兵。仁城之与谋明矣。昔管叔。成王之叔父也。与武庚叛。周公诛之。子颓。惠王之叔父也。作乱。郑厉公诛之。叔带。襄王之叔父也。作乱。晋文公诛之。广陵王胥。宣帝之叔祖也。祝诅发觉。汉公卿请诛胥。宣帝命即讯。胥自杀。臣而叛君。不可以叔父贷之也。然则仁城者。今之臣子所必讨之也。今之为 社稷计者。所必有以处之者也。盖凶徒。所以为乱逆者。其意不过欲取富贵耳。欲执权柄耳。今世用人。惟贤才是取。苟其诚心为善。才德著闻。则自可得进用。苟其大贤也。则亦当至于大用。何乃自陷于乱逆之恶。以求万不可得之富贵乎。且虽不得富贵。为平常人老死。孰若为恶逆被极刑乎。凶人之性。喜乱乐祸每如此。传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光海之自绝于天。久矣。贼徒阴结凶党。拂举国之心。而欲力胜天。意其能成乎。天道福善祸淫。断不可诬。仁城之罪。悖逆人理。天所不与。凶徒推戴之谋相次发觉。咸就诛戮。李适举素鍊之兵万有馀众。至入京城。一战覆败。身首横分。家族尽歼。天之不助乱人亦明矣。适贼之后。又有弘耇。安知此后不更有阴谋如弘耇者乎。如更有之。其诳诱之辞。必更用前日贼徒之言。其凶人自生祸心。自造乱谋
募兵。仁城之与谋明矣。昔管叔。成王之叔父也。与武庚叛。周公诛之。子颓。惠王之叔父也。作乱。郑厉公诛之。叔带。襄王之叔父也。作乱。晋文公诛之。广陵王胥。宣帝之叔祖也。祝诅发觉。汉公卿请诛胥。宣帝命即讯。胥自杀。臣而叛君。不可以叔父贷之也。然则仁城者。今之臣子所必讨之也。今之为 社稷计者。所必有以处之者也。盖凶徒。所以为乱逆者。其意不过欲取富贵耳。欲执权柄耳。今世用人。惟贤才是取。苟其诚心为善。才德著闻。则自可得进用。苟其大贤也。则亦当至于大用。何乃自陷于乱逆之恶。以求万不可得之富贵乎。且虽不得富贵。为平常人老死。孰若为恶逆被极刑乎。凶人之性。喜乱乐祸每如此。传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光海之自绝于天。久矣。贼徒阴结凶党。拂举国之心。而欲力胜天。意其能成乎。天道福善祸淫。断不可诬。仁城之罪。悖逆人理。天所不与。凶徒推戴之谋相次发觉。咸就诛戮。李适举素鍊之兵万有馀众。至入京城。一战覆败。身首横分。家族尽歼。天之不助乱人亦明矣。适贼之后。又有弘耇。安知此后不更有阴谋如弘耇者乎。如更有之。其诳诱之辞。必更用前日贼徒之言。其凶人自生祸心。自造乱谋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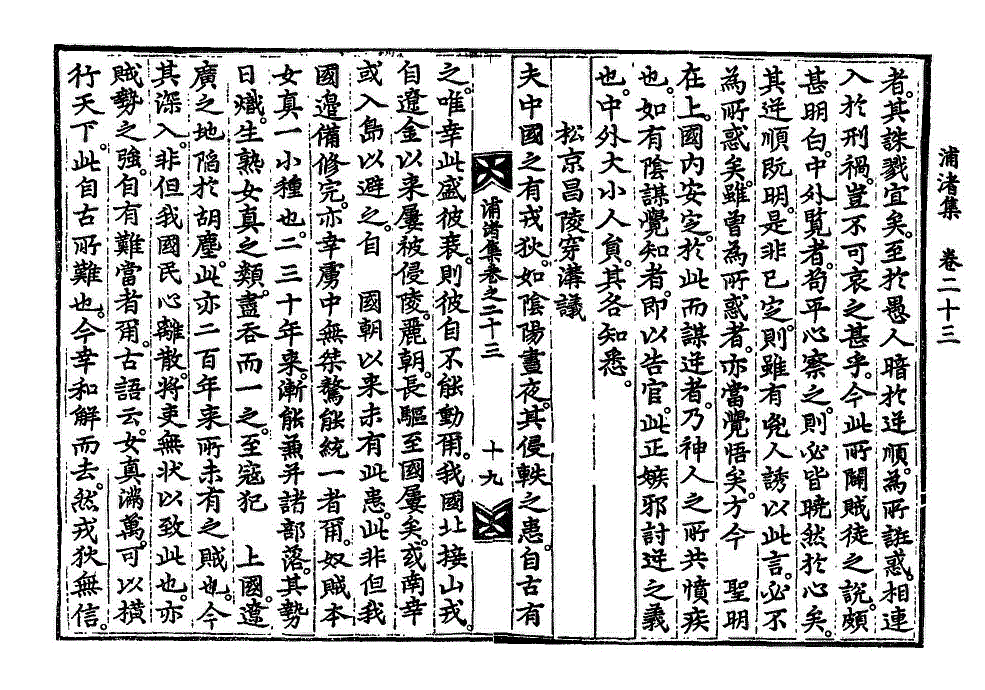 者。其诛戮宜矣。至于愚人暗于逆顺。为所诳惑。相连入于刑祸。岂不可哀之甚乎。今此所辟贼徒之说。颇甚明白。中外览者。苟平心察之。则必皆晓然于心矣。其逆顺既明。是非已定。则虽有凶人诱以此言。必不为所惑矣。虽曾为所惑者。亦当觉悟矣。方今 圣明在上。国内安定。于此而谋逆者。乃神人之所共愤疾也。如有阴谋觉知者。即以告官。此正嫉邪讨逆之义也。中外大小人员。其各知悉。
者。其诛戮宜矣。至于愚人暗于逆顺。为所诳惑。相连入于刑祸。岂不可哀之甚乎。今此所辟贼徒之说。颇甚明白。中外览者。苟平心察之。则必皆晓然于心矣。其逆顺既明。是非已定。则虽有凶人诱以此言。必不为所惑矣。虽曾为所惑者。亦当觉悟矣。方今 圣明在上。国内安定。于此而谋逆者。乃神人之所共愤疾也。如有阴谋觉知者。即以告官。此正嫉邪讨逆之义也。中外大小人员。其各知悉。松京昌陵穿沟议
夫中国之有戎狄。如阴阳昼夜。其侵轶之患。自古有之。唯幸此盛彼衰。则彼自不能动尔。我国北接山戎。自辽金以来屡被侵陵。丽朝。长驱至国屡矣。或南幸或入岛以避之。自 国朝以来未有此患。此非但我国边备修完。亦幸虏中无桀骜能统一者尔。奴贼本女真一小种也。二三十年来。渐能兼并诸部落。其势日炽。生熟女真之类。尽吞而一之。至寇犯 上国。辽广之地陷于胡尘。此亦二百年来所未有之贼也。今其深入。非但我国民心离散。将吏无状以致此也。亦贼势之强。自有难当者尔。古语云。女真满万。可以横行天下。此自古所难也。今幸和解而去。然戎狄无信。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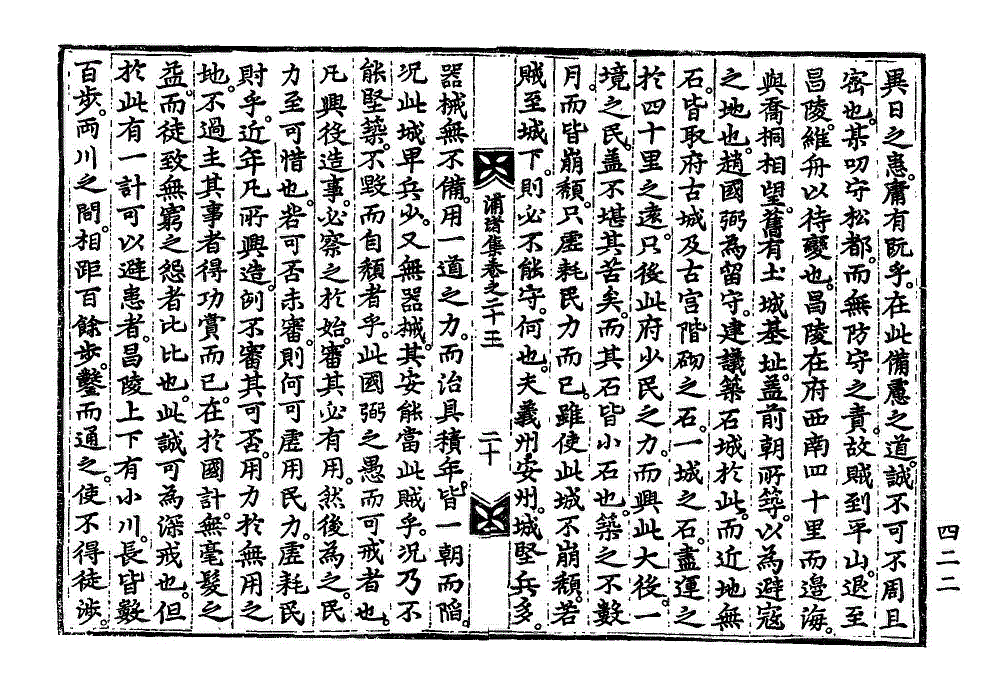 异日之患。庸有既乎。在此备虑之道。诚不可不周且密也。某叨守松都。而无防守之责。故贼到平山。退至昌陵。维舟以待变也。昌陵在府西南四十里而边海。与乔桐相望。旧有土城基址。盖前朝所筑。以为避寇之地也。赵国弼为留守。建议筑石城于此。而近地无石。皆取府古城及古宫阶砌之石。一城之石。尽运之于四十里之远。只役此府少民之力。而兴此大役。一境之民。盖不堪其苦矣。而其石皆小石也。筑之不数月。而皆崩颓。只虚耗民力而已。虽使此城不崩颓。若贼至城下。则必不能守。何也。夫义州,安州。城坚兵多。器械无不备。用一道之力。而治具积年。皆一朝而陷。况此城卑兵少。又无器械。其安能当此贼乎。况乃不能坚筑。不毁而自颓者乎。此国弼之愚而可戒者也。凡兴役造事。必察之于始。审其必有用。然后为之。民力至可惜也。若可否未审。则何可虚用民力。虚耗民财乎。近年凡所兴造。例不审其可否。用力于无用之地。不过主其事者得功赏而已。在于国计。无毫发之益。而徒致无穷之怨者比比也。此诚可为深戒也。但于此有一计可以避患者。昌陵上下有小川。长皆数百步。两川之间。相距百馀步。凿而通之。使不得徒涉。
异日之患。庸有既乎。在此备虑之道。诚不可不周且密也。某叨守松都。而无防守之责。故贼到平山。退至昌陵。维舟以待变也。昌陵在府西南四十里而边海。与乔桐相望。旧有土城基址。盖前朝所筑。以为避寇之地也。赵国弼为留守。建议筑石城于此。而近地无石。皆取府古城及古宫阶砌之石。一城之石。尽运之于四十里之远。只役此府少民之力。而兴此大役。一境之民。盖不堪其苦矣。而其石皆小石也。筑之不数月。而皆崩颓。只虚耗民力而已。虽使此城不崩颓。若贼至城下。则必不能守。何也。夫义州,安州。城坚兵多。器械无不备。用一道之力。而治具积年。皆一朝而陷。况此城卑兵少。又无器械。其安能当此贼乎。况乃不能坚筑。不毁而自颓者乎。此国弼之愚而可戒者也。凡兴役造事。必察之于始。审其必有用。然后为之。民力至可惜也。若可否未审。则何可虚用民力。虚耗民财乎。近年凡所兴造。例不审其可否。用力于无用之地。不过主其事者得功赏而已。在于国计。无毫发之益。而徒致无穷之怨者比比也。此诚可为深戒也。但于此有一计可以避患者。昌陵上下有小川。长皆数百步。两川之间。相距百馀步。凿而通之。使不得徒涉。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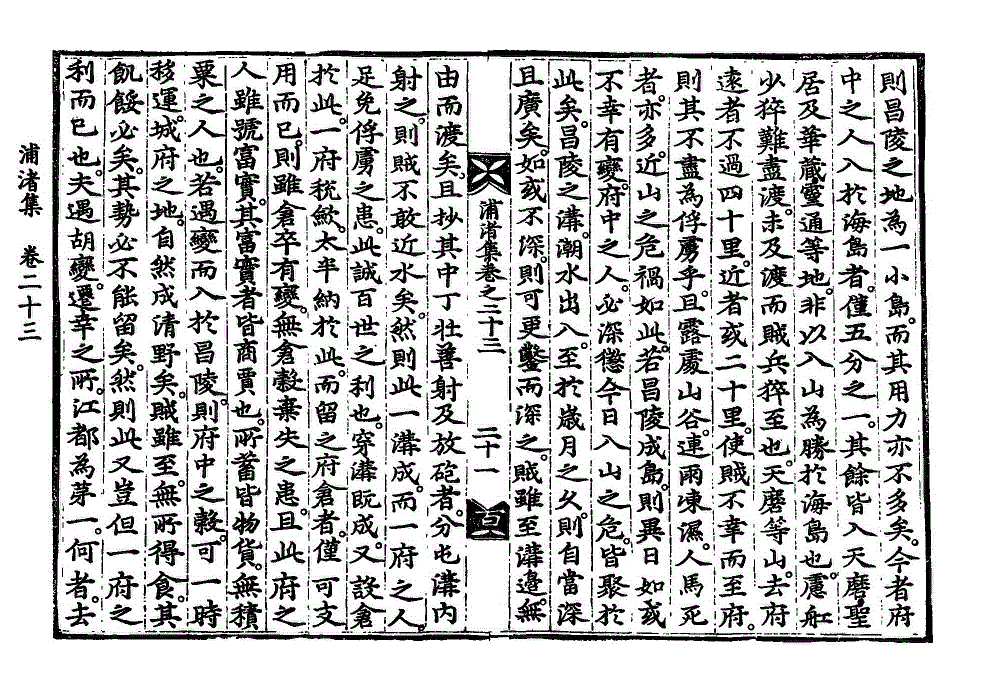 则昌陵之地为一小岛。而其用力亦不多矣。今者府中之人入于海岛者。仅五分之一。其馀皆入天磨,圣居及华藏,灵通等地。非以入山为胜于海岛也。虑船少猝难尽渡。未及渡而贼兵猝至也。天磨等山。去府远者不过四十里。近者或二十里。使贼不幸而至府。则其不尽为俘虏乎。且露处山谷。连雨冻湿。人马死者。亦多。近山之危祸如此。若昌陵成岛。则异日如或不幸有变。府中之人。必深惩今日入山之危。皆聚于此矣。昌陵之沟。潮水出入。至于岁月之久。则自当深且广矣。如或不深。则可更凿而深之。贼虽至沟边。无由而渡矣。且抄其中丁壮善射及放炮者。分屯沟内射之。则贼不敢近水矣。然则此一沟成。而一府之人。足免俘虏之患。此诚百世之利也。穿沟既成。又设仓于此。一府税敛。太半纳于此。而留之府仓者。仅可支用而已。则虽仓卒有变。无仓谷弃失之患。且此府之人虽号富实。其富实者皆商贾也。所蓄皆物货。无积粟之人也。若遇变而入于昌陵。则府中之谷。可一时移运。城府之地。自然成清野矣。贼虽至。无所得食。其饥馁必矣。其势必不能留矣。然则此又岂但一府之利而已也。夫遇胡变。迁幸之所。江都为第一。何者。去
则昌陵之地为一小岛。而其用力亦不多矣。今者府中之人入于海岛者。仅五分之一。其馀皆入天磨,圣居及华藏,灵通等地。非以入山为胜于海岛也。虑船少猝难尽渡。未及渡而贼兵猝至也。天磨等山。去府远者不过四十里。近者或二十里。使贼不幸而至府。则其不尽为俘虏乎。且露处山谷。连雨冻湿。人马死者。亦多。近山之危祸如此。若昌陵成岛。则异日如或不幸有变。府中之人。必深惩今日入山之危。皆聚于此矣。昌陵之沟。潮水出入。至于岁月之久。则自当深且广矣。如或不深。则可更凿而深之。贼虽至沟边。无由而渡矣。且抄其中丁壮善射及放炮者。分屯沟内射之。则贼不敢近水矣。然则此一沟成。而一府之人。足免俘虏之患。此诚百世之利也。穿沟既成。又设仓于此。一府税敛。太半纳于此。而留之府仓者。仅可支用而已。则虽仓卒有变。无仓谷弃失之患。且此府之人虽号富实。其富实者皆商贾也。所蓄皆物货。无积粟之人也。若遇变而入于昌陵。则府中之谷。可一时移运。城府之地。自然成清野矣。贼虽至。无所得食。其饥馁必矣。其势必不能留矣。然则此又岂但一府之利而已也。夫遇胡变。迁幸之所。江都为第一。何者。去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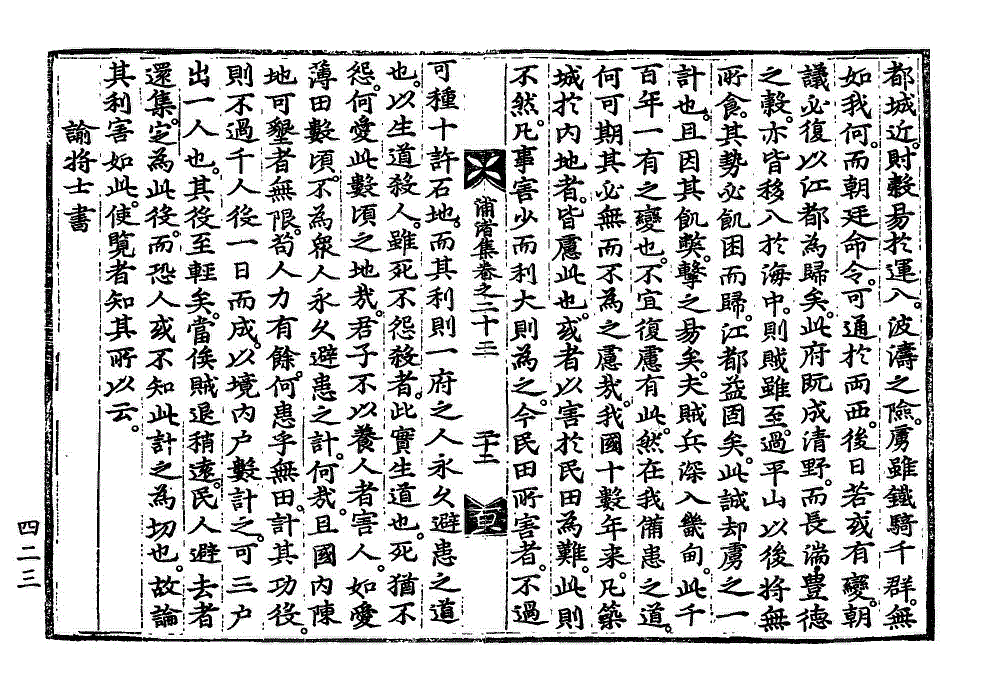 都城近。财谷易于运入。波涛之险。虏虽铁骑千群。无如我何。而朝廷命令。可通于两西。后日若或有变。朝议必复以江都为归矣。此府既成清野。而长湍,丰德之谷。亦皆移入于海中。则贼虽至。过平山以后将无所食。其势必饥困而归。江都益固矣。此诚却虏之一计也。且因其饥弊。击之易矣。夫贼兵深入畿甸。此千百年一有之变也。不宜复虑有此。然在我备患之道。何可期其必无而不为之虑哉。我国十数年来。凡筑城于内地者。皆虑此也。或者以害于民田为难。此则不然。凡事害少而利大则为之。今民田所害者。不过可种十许石地。而其利则一府之人永久避患之道也。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者。此实生道也。死犹不怨。何爱此数顷之地哉。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如爱薄田数顷。不为众人永久避患之计。何哉。且国内陈地可垦者无限。苟人力有馀。何患乎无田。计其功役。则不过千人役一日而成。以境内户数计之。可三户出一人也。其役至轻矣。当俟贼退稍远。民人避去者还集。定为此役。而恐人或不知此计之为切也。故论其利害如此。使览者知其所以云。
都城近。财谷易于运入。波涛之险。虏虽铁骑千群。无如我何。而朝廷命令。可通于两西。后日若或有变。朝议必复以江都为归矣。此府既成清野。而长湍,丰德之谷。亦皆移入于海中。则贼虽至。过平山以后将无所食。其势必饥困而归。江都益固矣。此诚却虏之一计也。且因其饥弊。击之易矣。夫贼兵深入畿甸。此千百年一有之变也。不宜复虑有此。然在我备患之道。何可期其必无而不为之虑哉。我国十数年来。凡筑城于内地者。皆虑此也。或者以害于民田为难。此则不然。凡事害少而利大则为之。今民田所害者。不过可种十许石地。而其利则一府之人永久避患之道也。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者。此实生道也。死犹不怨。何爱此数顷之地哉。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如爱薄田数顷。不为众人永久避患之计。何哉。且国内陈地可垦者无限。苟人力有馀。何患乎无田。计其功役。则不过千人役一日而成。以境内户数计之。可三户出一人也。其役至轻矣。当俟贼退稍远。民人避去者还集。定为此役。而恐人或不知此计之为切也。故论其利害如此。使览者知其所以云。谕将士书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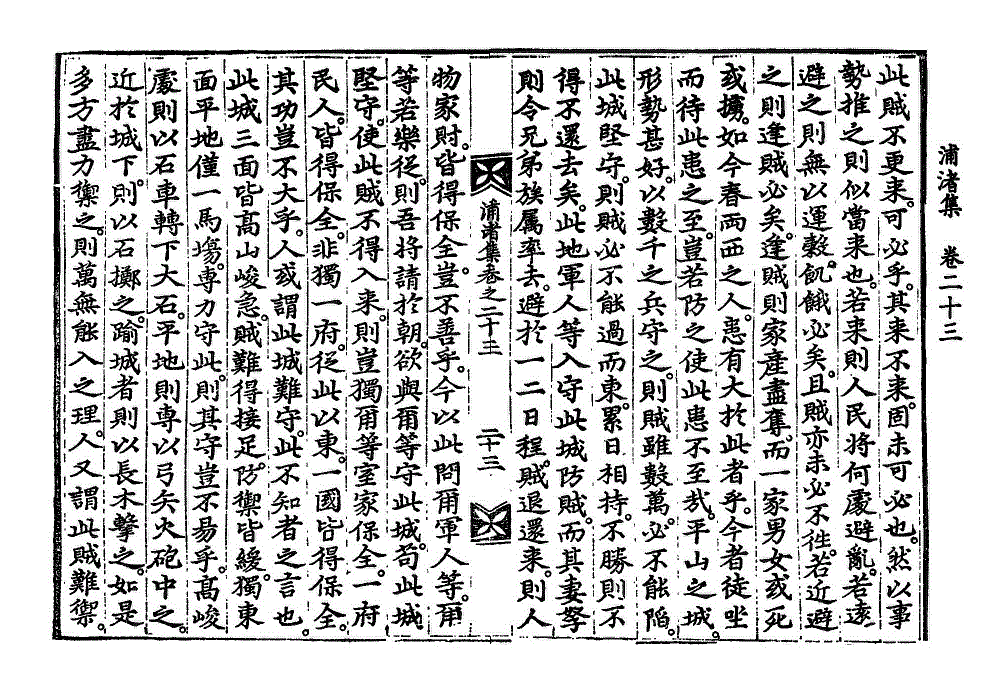 此贼不更来。可必乎。其来不来。固未可必也。然以事势推之则似当来也。若来则人民将何处避乱。若远避之则无以运谷。饥饿必矣。且贼亦未必不往。若近避之则逢贼必矣。逢贼则家产尽夺。而一家男女或死或掳。如今春两西之人。患有大于此者乎。今者徒坐而待此患之至。岂若防之使此患不至哉。平山之城。形势甚好。以数千之兵守之。则贼虽数万。必不能陷。此城坚守。则贼必不能过而东。累日相持。不胜则不得不还去矣。此地军人等入守此城防贼。而其妻孥则令兄弟族属率去。避于一二日程。贼退还来。则人物家财。皆得保全。岂不善乎。今以此问尔军人等。尔等若乐从。则吾将请于朝。欲与尔等守此城。苟此城坚守。使此贼不得入来。则岂独尔等室家保全。一府民人。皆得保全。非独一府。从此以东。一国皆得保全。其功岂不大乎。人或谓此城难守。此不知者之言也。此城三面皆高山峻急。贼难得接足。防御皆缓。独东面平地仅一马场。专力守此。则其守岂不易乎。高峻处则以石车转下大石。平地则专以弓矢火炮中之。近于城下。则以石掷之。踰城者则以长木击之。如是多方尽力御之。则万无能入之理。人又谓此贼难御。
此贼不更来。可必乎。其来不来。固未可必也。然以事势推之则似当来也。若来则人民将何处避乱。若远避之则无以运谷。饥饿必矣。且贼亦未必不往。若近避之则逢贼必矣。逢贼则家产尽夺。而一家男女或死或掳。如今春两西之人。患有大于此者乎。今者徒坐而待此患之至。岂若防之使此患不至哉。平山之城。形势甚好。以数千之兵守之。则贼虽数万。必不能陷。此城坚守。则贼必不能过而东。累日相持。不胜则不得不还去矣。此地军人等入守此城防贼。而其妻孥则令兄弟族属率去。避于一二日程。贼退还来。则人物家财。皆得保全。岂不善乎。今以此问尔军人等。尔等若乐从。则吾将请于朝。欲与尔等守此城。苟此城坚守。使此贼不得入来。则岂独尔等室家保全。一府民人。皆得保全。非独一府。从此以东。一国皆得保全。其功岂不大乎。人或谓此城难守。此不知者之言也。此城三面皆高山峻急。贼难得接足。防御皆缓。独东面平地仅一马场。专力守此。则其守岂不易乎。高峻处则以石车转下大石。平地则专以弓矢火炮中之。近于城下。则以石掷之。踰城者则以长木击之。如是多方尽力御之。则万无能入之理。人又谓此贼难御。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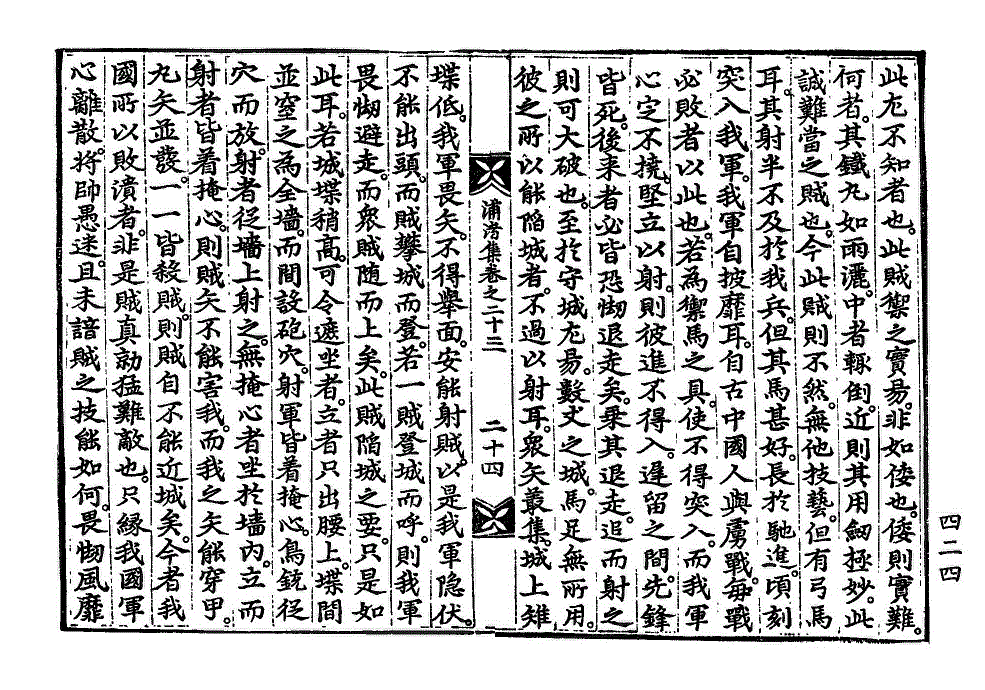 此尤不知者也。此贼御之实易。非如倭也。倭则实难。何者。其铁丸如雨洒。中者辄倒。近则其用剑极妙。此诚难当之贼也。今此贼则不然。无他技艺。但有弓马耳。其射半不及于我兵。但其马甚好。长于驰进。顷刻突入我军。我军自披靡耳。自古中国人与虏战。每战必败者以此也。若为御马之具。使不得突入。而我军心定不挠。坚立以射。则彼进不得入。迟留之间。先锋皆死。后来者必皆恐怯退走矣。乘其退走。追而射之则可大破也。至于守城尤易。数丈之城。马足无所用。彼之所以能陷城者。不过以射耳。众矢丛集。城上雉堞低。我军畏矢。不得举面。安能射贼。以是我军隐伏。不能出头。而贼攀城而登。若一贼登城而呼。则我军畏怯避走。而众贼随而上矣。此贼陷城之要。只是如此耳。若城堞稍高。可令遮坐者。立者只出腰上。堞间并窒之为全墙。而间设炮穴。射军皆着掩心。鸟铳从穴而放。射者从墙上射之。无掩心者坐于墙内。立而射者皆着掩心。则贼矢不能害我。而我之矢能穿甲。丸矢并发。一一皆杀贼。则贼自不能近城矣。今者我国所以败溃者。非是贼真勍猛难敌也。只缘我国军心离散。将帅愚迷。且未谙贼之技能如何。畏怯风靡
此尤不知者也。此贼御之实易。非如倭也。倭则实难。何者。其铁丸如雨洒。中者辄倒。近则其用剑极妙。此诚难当之贼也。今此贼则不然。无他技艺。但有弓马耳。其射半不及于我兵。但其马甚好。长于驰进。顷刻突入我军。我军自披靡耳。自古中国人与虏战。每战必败者以此也。若为御马之具。使不得突入。而我军心定不挠。坚立以射。则彼进不得入。迟留之间。先锋皆死。后来者必皆恐怯退走矣。乘其退走。追而射之则可大破也。至于守城尤易。数丈之城。马足无所用。彼之所以能陷城者。不过以射耳。众矢丛集。城上雉堞低。我军畏矢。不得举面。安能射贼。以是我军隐伏。不能出头。而贼攀城而登。若一贼登城而呼。则我军畏怯避走。而众贼随而上矣。此贼陷城之要。只是如此耳。若城堞稍高。可令遮坐者。立者只出腰上。堞间并窒之为全墙。而间设炮穴。射军皆着掩心。鸟铳从穴而放。射者从墙上射之。无掩心者坐于墙内。立而射者皆着掩心。则贼矢不能害我。而我之矢能穿甲。丸矢并发。一一皆杀贼。则贼自不能近城矣。今者我国所以败溃者。非是贼真勍猛难敌也。只缘我国军心离散。将帅愚迷。且未谙贼之技能如何。畏怯风靡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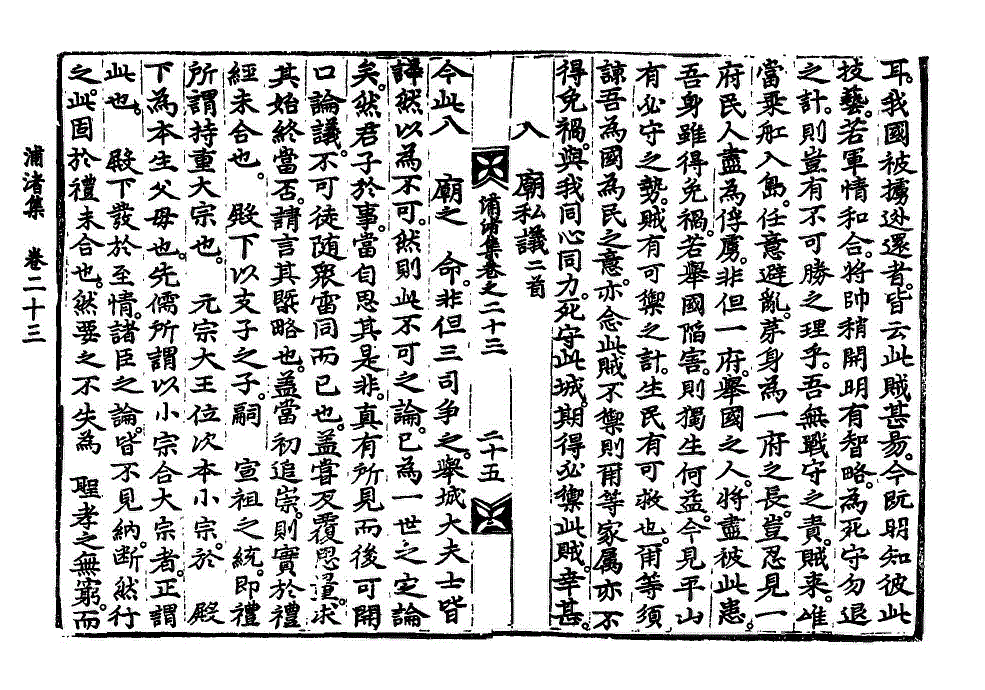 耳。我国被掳逃还者。皆云此贼甚易。今既明知彼此技艺。若军情和合。将帅稍开明有智略。为死守勿退之计。则岂有不可胜之理乎。吾无战守之责。贼来。唯当乘船入岛。任意避乱。第身为一府之长。岂忍见一府民人尽为俘虏。非但一府。举国之人。将尽被此患。吾身虽得免祸。若举国陷害。则独生何益。今见平山有必守之势。贼有可御之计。生民有可救也。尔等须谅吾为国为民之意。亦念此贼不御则尔等家属亦不得免祸。与我同心同力。死守此城。期得必御此贼。幸甚。
耳。我国被掳逃还者。皆云此贼甚易。今既明知彼此技艺。若军情和合。将帅稍开明有智略。为死守勿退之计。则岂有不可胜之理乎。吾无战守之责。贼来。唯当乘船入岛。任意避乱。第身为一府之长。岂忍见一府民人尽为俘虏。非但一府。举国之人。将尽被此患。吾身虽得免祸。若举国陷害。则独生何益。今见平山有必守之势。贼有可御之计。生民有可救也。尔等须谅吾为国为民之意。亦念此贼不御则尔等家属亦不得免祸。与我同心同力。死守此城。期得必御此贼。幸甚。入 庙私议(二首)
今此入 庙之 命。非但三司争之。举城大夫士皆哗然以为不可。然则此不可之论。已为一世之定论矣。然君子于事。当自思其是非。真有所见而后可开口论议。不可徒随众雷同而已也。盖尝反覆思量。求其始终当否。请言其槩略也。盖当初追崇。则实于礼经未合也。 殿下以支子之子。嗣 宣祖之统。即礼所谓持重大宗也。 元宗大王位次本小宗。于 殿下为本生父母也。先儒所谓以小宗合大宗者。正谓此也。 殿下发于至情。诸臣之论。皆不见纳。断然行之。此固于礼未合也。然要之不失为 圣孝之无穷。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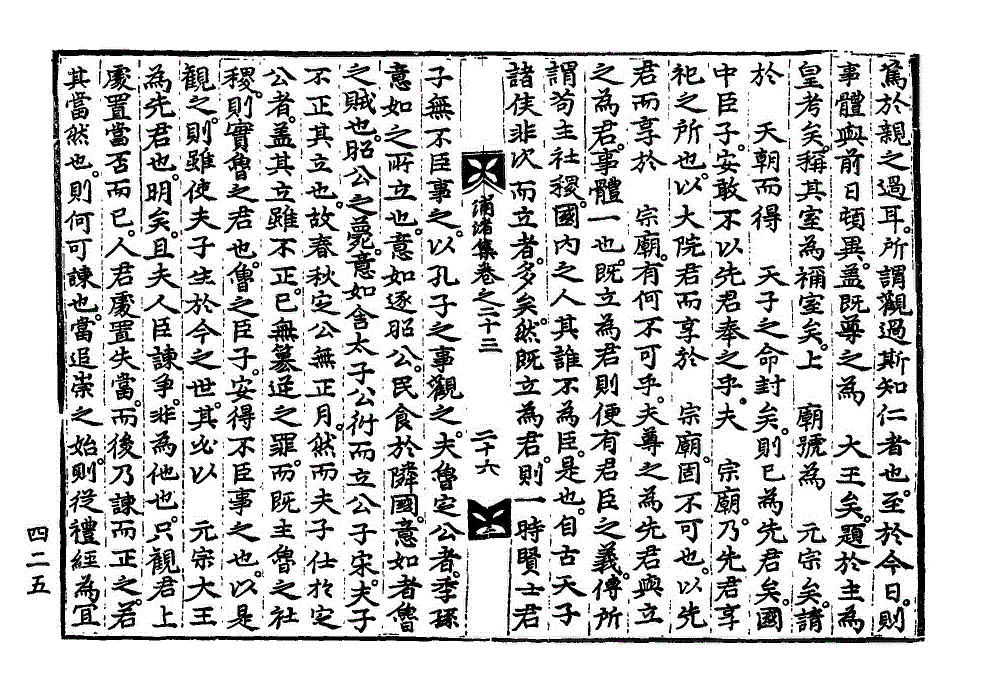 笃于亲之过耳。所谓观过斯知仁者也。至于今日。则事体与前日顿异。盖既尊之为 大王矣。题于主为皇考矣。称其室为祢室矣。上 庙号为 元宗矣。请于 天朝而得 天子之命封矣。则已为先君矣。国中臣子。安敢不以先君奉之乎。夫 宗庙。乃先君享祀之所也。以大院君而享于 宗庙。固不可也。以先君而享于 宗庙。有何不可乎。夫尊之为先君与立之为君。事体一也。既立为君则便有君臣之义。传所谓苟主社稷。国内之人其谁不为臣。是也。自古天子诸侯非次而立者。多矣。然既立为君。则一时贤士君子无不臣事之。以孔子之事观之。夫鲁定公者。季孙意如之所立也。意如逐昭公。民食于邻国。意如者鲁之贼也。昭公之薨。意如舍太子公衍而立公子宋。夫子不正其立也。故春秋定公无正月。然而夫子仕于定公者。盖其立虽不正。已无篡逆之罪。而既主鲁之社稷。则实鲁之君也。鲁之臣子。安得不臣事之也。以是观之。则虽使夫子生于今之世。其必以 元宗大王为先君也。明矣。且夫人臣谏争。非为他也。只观君上处置当否而已。人君处置失当。而后乃谏而正之。若其当然也。则何可谏也。当追崇之始。则从礼经为宜
笃于亲之过耳。所谓观过斯知仁者也。至于今日。则事体与前日顿异。盖既尊之为 大王矣。题于主为皇考矣。称其室为祢室矣。上 庙号为 元宗矣。请于 天朝而得 天子之命封矣。则已为先君矣。国中臣子。安敢不以先君奉之乎。夫 宗庙。乃先君享祀之所也。以大院君而享于 宗庙。固不可也。以先君而享于 宗庙。有何不可乎。夫尊之为先君与立之为君。事体一也。既立为君则便有君臣之义。传所谓苟主社稷。国内之人其谁不为臣。是也。自古天子诸侯非次而立者。多矣。然既立为君。则一时贤士君子无不臣事之。以孔子之事观之。夫鲁定公者。季孙意如之所立也。意如逐昭公。民食于邻国。意如者鲁之贼也。昭公之薨。意如舍太子公衍而立公子宋。夫子不正其立也。故春秋定公无正月。然而夫子仕于定公者。盖其立虽不正。已无篡逆之罪。而既主鲁之社稷。则实鲁之君也。鲁之臣子。安得不臣事之也。以是观之。则虽使夫子生于今之世。其必以 元宗大王为先君也。明矣。且夫人臣谏争。非为他也。只观君上处置当否而已。人君处置失当。而后乃谏而正之。若其当然也。则何可谏也。当追崇之始。则从礼经为宜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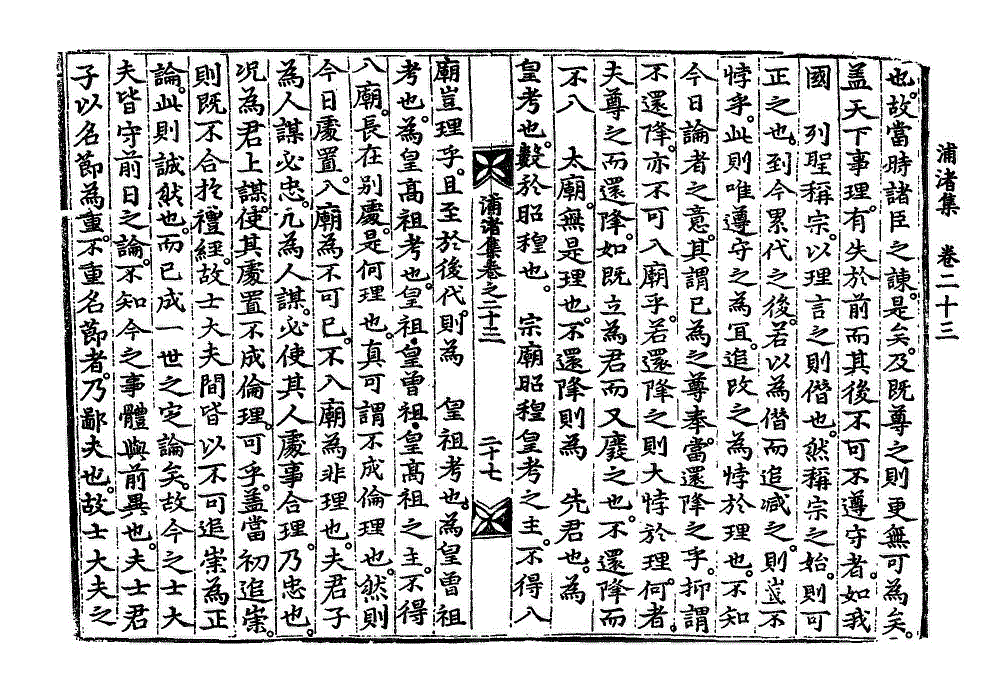 也。故当时诸臣之谏。是矣。及既尊之则更无可为矣。盖天下事理。有失于前而其后不可不遵守者。如我国 列圣称宗。以理言之则僭也。然称宗之始。则可正之也。到今累代之后。若以为僭而追减之。则岂不悖乎。此则唯遵守之为宜。追改之为悖于理也。不知今日论者之意。其谓已为之尊奉。当还降之乎。抑谓不还降。亦不可入庙乎。若还降之则大悖于理。何者。夫尊之而还降。如既立为君而又废之也。不还降而不入 太庙。无是理也。不还降则为 先君也。为 皇考也。数于昭穆也。 宗庙昭穆皇考之主。不得入庙岂理乎。且至于后代。则为 皇祖考也。为皇曾祖考也。为皇高祖考也。皇祖,皇曾祖,皇高祖之主。不得入庙。长在别处。是何理也。真可谓不成伦理也。然则今日处置。入庙为不可已。不入庙为非理也。夫君子为人谋必忠。凡为人谋。必使其人处事合理。乃忠也。况为君上谋。使其处置不成伦理。可乎。盖当初追崇。则既不合于礼经。故士大夫间皆以不可追崇为正论。此则诚然也。而已成一世之定论矣。故今之士大夫皆守前日之论。不知今之事体与前异也。夫士君子以名节为重。不重名节者。乃鄙夫也。故士大夫之
也。故当时诸臣之谏。是矣。及既尊之则更无可为矣。盖天下事理。有失于前而其后不可不遵守者。如我国 列圣称宗。以理言之则僭也。然称宗之始。则可正之也。到今累代之后。若以为僭而追减之。则岂不悖乎。此则唯遵守之为宜。追改之为悖于理也。不知今日论者之意。其谓已为之尊奉。当还降之乎。抑谓不还降。亦不可入庙乎。若还降之则大悖于理。何者。夫尊之而还降。如既立为君而又废之也。不还降而不入 太庙。无是理也。不还降则为 先君也。为 皇考也。数于昭穆也。 宗庙昭穆皇考之主。不得入庙岂理乎。且至于后代。则为 皇祖考也。为皇曾祖考也。为皇高祖考也。皇祖,皇曾祖,皇高祖之主。不得入庙。长在别处。是何理也。真可谓不成伦理也。然则今日处置。入庙为不可已。不入庙为非理也。夫君子为人谋必忠。凡为人谋。必使其人处事合理。乃忠也。况为君上谋。使其处置不成伦理。可乎。盖当初追崇。则既不合于礼经。故士大夫间皆以不可追崇为正论。此则诚然也。而已成一世之定论矣。故今之士大夫皆守前日之论。不知今之事体与前异也。夫士君子以名节为重。不重名节者。乃鄙夫也。故士大夫之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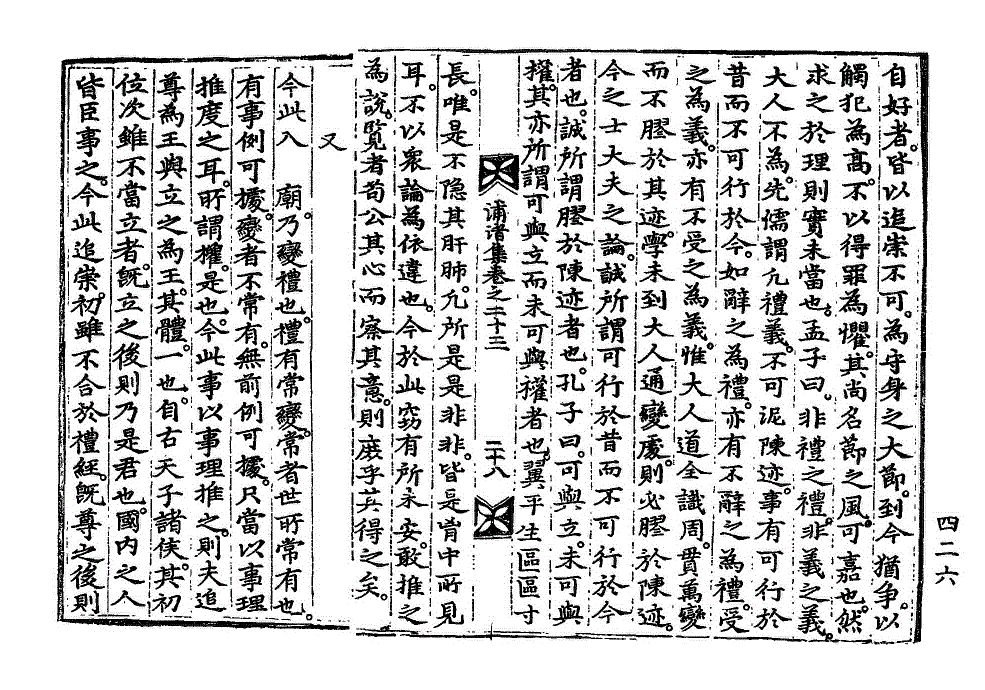 自好者。皆以追崇不可。为守身之大节。到今犹争。以触犯为高。不以得罪为惧。其尚名节之风。可嘉也。然求之于理则实未当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先濡谓凡礼义。不可泥陈迹。事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如辞之为礼。亦有不辞之为礼。受之为义。亦有不受之为义。惟大人道全识周。贯万变而不胶于其迹。学未到大人通变处。则必胶于陈迹。今之士大夫之论。诚所谓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者也。诚所谓胶于陈迹者也。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其亦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也。翼平生区区寸长。唯是不隐其肝肺。凡所是是非非。皆是胸中所见耳。不以众论为依违也。今于此窃有所未安。敢推之为说。览者苟公其心而察其意。则庶乎其得之矣。
自好者。皆以追崇不可。为守身之大节。到今犹争。以触犯为高。不以得罪为惧。其尚名节之风。可嘉也。然求之于理则实未当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先濡谓凡礼义。不可泥陈迹。事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如辞之为礼。亦有不辞之为礼。受之为义。亦有不受之为义。惟大人道全识周。贯万变而不胶于其迹。学未到大人通变处。则必胶于陈迹。今之士大夫之论。诚所谓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者也。诚所谓胶于陈迹者也。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其亦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也。翼平生区区寸长。唯是不隐其肝肺。凡所是是非非。皆是胸中所见耳。不以众论为依违也。今于此窃有所未安。敢推之为说。览者苟公其心而察其意。则庶乎其得之矣。入 庙私议
今此入 庙。乃变礼也。礼有常变。常者世所常有也。有事例可据。变者不常有。无前例可据。只当以事理推度之耳。所谓权。是也。今此事以事理推之。则夫追尊为王与立之为王。其体。一也。自古天子诸侯。其初位次虽不当立者。既立之后则乃是君也。国内之人皆臣事之。今此追崇。初虽不合于礼经。既尊之后则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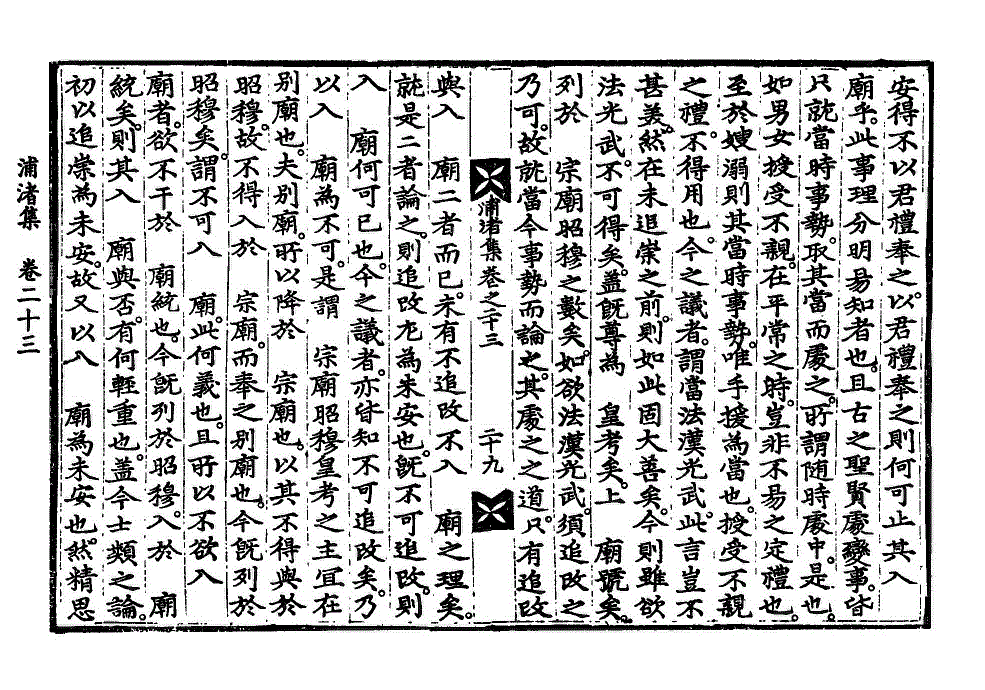 安得不以君礼奉之。以君礼奉之则何可止其入 庙乎。此事理分明易知者也。且古之圣贤处变事。皆只就当时事势。取其当而处之。所谓随时处中。是也。如男女授受不亲。在平常之时。岂非不易之定礼也。至于嫂溺则其当时事势。唯手援为当也。授受不亲之礼。不得用也。今之议者。谓当法汉光武。此言岂不甚美。然在未追崇之前。则如此固大善矣。今则虽欲法光武。不可得矣。盖既尊为 皇考矣。上 庙号矣。列于 宗庙昭穆之数矣。如欲法汉光武。须追改之乃可。故就当今事势而论之。其处之之道。只有追改与入 庙二者而已。未有不追改不入 庙之理矣。就是二者论之。则追改尤为未安也。既不可追改。则入 庙何可已也。今之议者。亦皆知不可追改矣。乃以入 庙为不可。是谓 宗庙昭穆皇考之主宜在别庙也。夫别庙。所以降于 宗庙也。以其不得与于昭穆。故不得入于 宗庙。而奉之别庙也。今既列于昭穆矣。谓不可入 庙。此何义也。且所以不欲入 庙者。欲不干于 庙统也。今既列于昭穆。入于 庙统矣。则其入 庙与否。有何轻重也。盖今士类之论。初以追崇为未安。故又以入 庙为未安也。然精思
安得不以君礼奉之。以君礼奉之则何可止其入 庙乎。此事理分明易知者也。且古之圣贤处变事。皆只就当时事势。取其当而处之。所谓随时处中。是也。如男女授受不亲。在平常之时。岂非不易之定礼也。至于嫂溺则其当时事势。唯手援为当也。授受不亲之礼。不得用也。今之议者。谓当法汉光武。此言岂不甚美。然在未追崇之前。则如此固大善矣。今则虽欲法光武。不可得矣。盖既尊为 皇考矣。上 庙号矣。列于 宗庙昭穆之数矣。如欲法汉光武。须追改之乃可。故就当今事势而论之。其处之之道。只有追改与入 庙二者而已。未有不追改不入 庙之理矣。就是二者论之。则追改尤为未安也。既不可追改。则入 庙何可已也。今之议者。亦皆知不可追改矣。乃以入 庙为不可。是谓 宗庙昭穆皇考之主宜在别庙也。夫别庙。所以降于 宗庙也。以其不得与于昭穆。故不得入于 宗庙。而奉之别庙也。今既列于昭穆矣。谓不可入 庙。此何义也。且所以不欲入 庙者。欲不干于 庙统也。今既列于昭穆。入于 庙统矣。则其入 庙与否。有何轻重也。盖今士类之论。初以追崇为未安。故又以入 庙为未安也。然精思浦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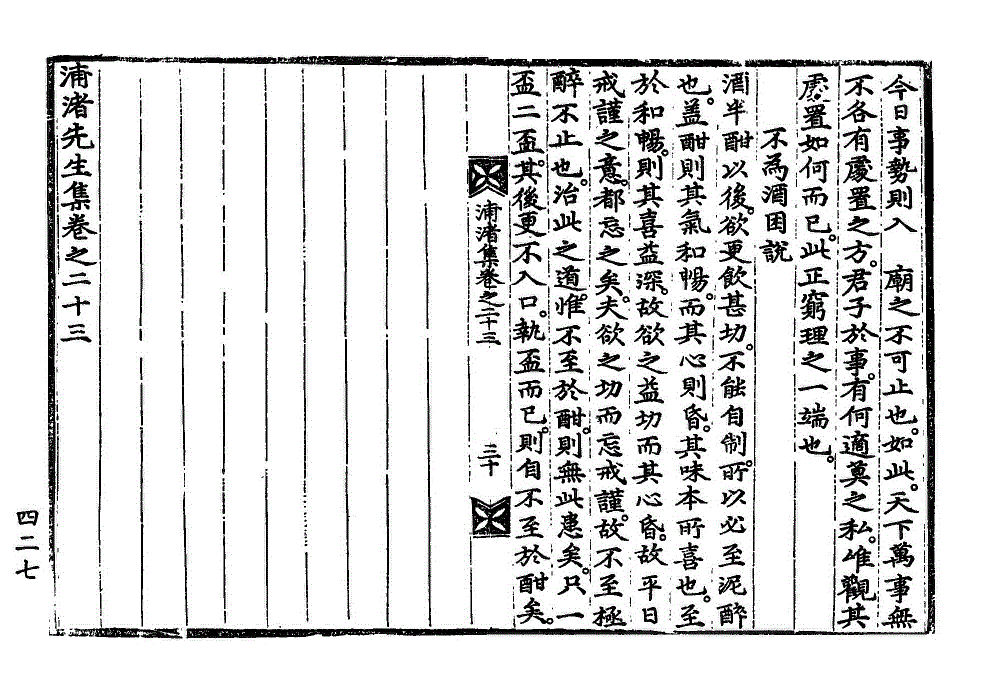 今日事势则入 庙之不可止也。如此。天下万事无不各有处置之方。君子于事。有何适莫之私。唯观其处置如何而已。此正穷理之一端也。
今日事势则入 庙之不可止也。如此。天下万事无不各有处置之方。君子于事。有何适莫之私。唯观其处置如何而已。此正穷理之一端也。不为酒困说
酒半酣以后。欲更饮甚切。不能自制。所以必至泥醉也。盖酣则其气和畅。而其心则昏。其味本所喜也。至于和畅。则其喜益深。故欲之益切而其心昏。故平日戒谨之意。都忘之矣。夫欲之切而忘戒谨。故不至极醉不止也。治此之道。惟不至于酣。则无此患矣。只一杯二杯。其后更不入口。执杯而已。则自不至于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