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书(十一首)
书(十一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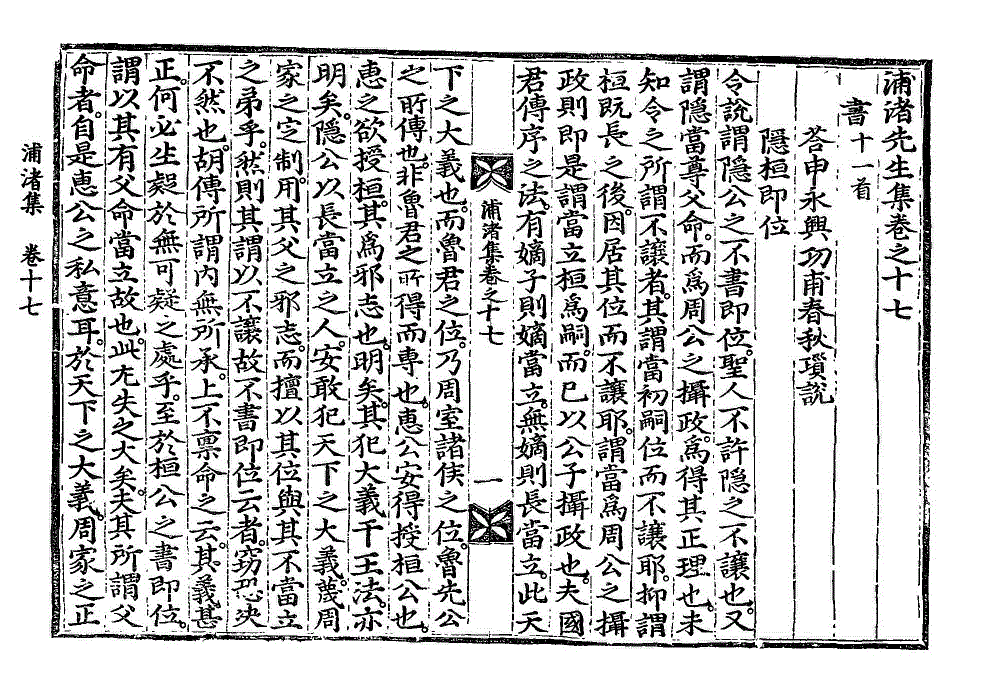 答申永兴功甫春秋琐说
答申永兴功甫春秋琐说隐桓即位
令说谓隐公之不书即位。圣人不许隐之不让也。又谓隐当尊父命。而为周公之摄政。为得其正理也。未知令之所谓不让者。其谓当初嗣位而不让耶。抑谓桓既长之后。因居其位而不让耶。谓当为周公之摄政则即是谓当立桓为嗣。而已以公子摄政也。夫国君传序之法。有嫡子则嫡当立。无嫡则长当立。此天下之大义也。而鲁君之位。乃周室诸侯之位。鲁先公之所传也。非鲁君之所得而专也。惠公安得授桓公也。惠之欲授桓。其为邪志也。明矣。其犯大义干王法。亦明矣。隐公以长当立之人。安敢犯天下之大义。蔑周家之定制。用其父之邪志。而擅以其位与其不当立之弟乎。然则其谓以不让故不书即位云者。窃恐决不然也。胡传所谓内无所承。上不禀命之云。其义甚正。何必生疑于无可疑之处乎。至于桓公之书即位。谓以其有父命当立故也。此尤失之大矣。夫其所谓父命者。自是惠公之私意耳。于天下之大义。周家之正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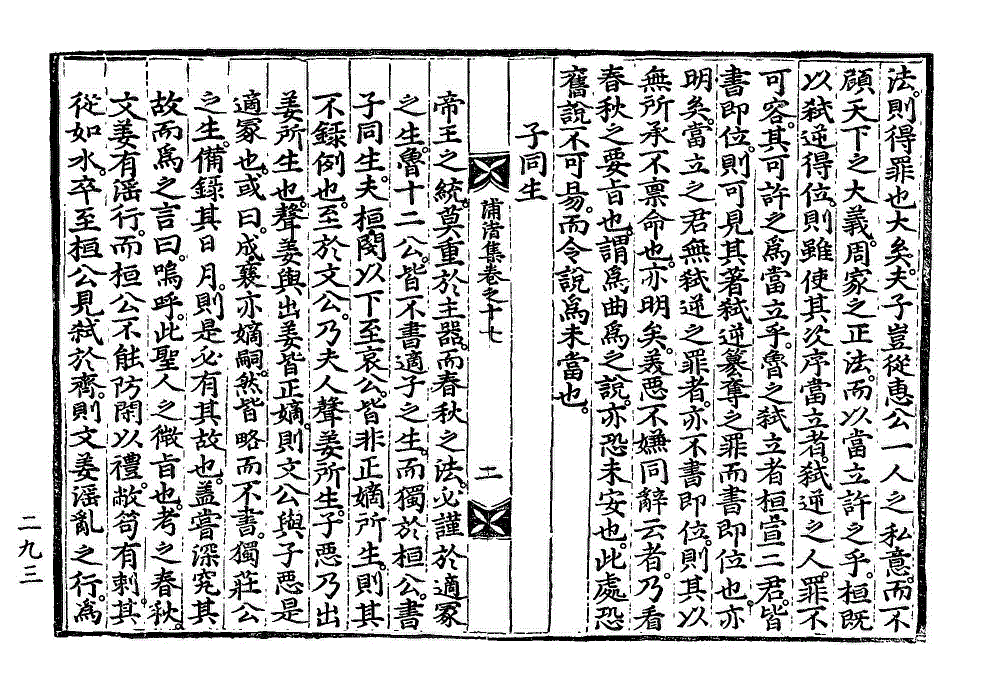 法。则得罪也大矣。夫子岂从惠公一人之私意。而不顾天下之大义。周家之正法。而以当立许之乎。桓既以弑逆得位。则虽使其次序当立者。弑逆之人。罪不可容。其可许之为当立乎。鲁之弑立者桓,宣二君。皆书即位。则可见其著弑逆篡夺之罪而书即位也。亦明矣。当立之君无弑逆之罪者。亦不书即位。则其以无所承不禀命也。亦明矣。美恶不嫌同辞云者。乃看春秋之要旨也。谓为曲为之说。亦恐未安也。此处恐旧说不可易。而令说为未当也。
法。则得罪也大矣。夫子岂从惠公一人之私意。而不顾天下之大义。周家之正法。而以当立许之乎。桓既以弑逆得位。则虽使其次序当立者。弑逆之人。罪不可容。其可许之为当立乎。鲁之弑立者桓,宣二君。皆书即位。则可见其著弑逆篡夺之罪而书即位也。亦明矣。当立之君无弑逆之罪者。亦不书即位。则其以无所承不禀命也。亦明矣。美恶不嫌同辞云者。乃看春秋之要旨也。谓为曲为之说。亦恐未安也。此处恐旧说不可易。而令说为未当也。子同生
帝王之统。莫重于主器。而春秋之法。必谨于适冢之生。鲁十二公。皆不书适子之生。而独于桓公。书子同生。夫桓,闵以下至哀公。皆非正嫡所生。则其不录例也。至于文公。乃夫人声姜所生。子恶乃出姜所生也。声姜与出姜皆正嫡。则文公与子恶是适冢也。或曰。成,襄亦嫡嗣。然皆略而不书。独庄公之生。备录其日月。则是必有其故也。盖尝深究其故而为之言曰。呜呼。此圣人之微旨也。考之春秋。文姜有淫行。而桓公不能防闲以礼。敝笱有刺。其从如水。卒至桓公见弑于齐。则文姜淫乱之行。为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4H 页
 二国之患。而子同之生。适当文姜居鲁之日。此圣人所以备录于经。是别嫌明微之意也。齐人之诗曰。展我甥兮。所以明为鲁公之子也。特书于经。亦犹齐诗之意也。圣人于删诗之际。所以存而不去。与鲁史之笔相为表里。其致谨于国储之生。至矣。惟后世昧于此义。故以吕易嬴而伯翳之祀忽诸。以牛易马而晋氏之宗乱真。可不谨哉。胡传谓适冢之生。即书于册(一作策)。与子之法也。经书子同生。所以明与子之法也。呜呼。此岂知圣人言外之旨乎。春秋之旨。果止于此乎。若止如胡氏之说。则圣人何以不书文公,子恶之生。而明与子之法乎。不书文公,子恶。而独书子同之生。则胡氏之说。可知其不然也。或曰。然则圣人不书文公,子恶之生。亦有说乎。曰有。此仲尼非徒不书之也。旧史必书之。而仲尼反削之也。何者。鲁之诸公。嫡子之生三也。庄,文与子恶是也。是皆正嫡之生而春秋一例书嫡子生。则夫人能之是不过史氏之凡例也后世何以知圣人别嫌明微之意也。必也削文公,子恶之生。而独书子同之生。然后有以启国人之问。而致后世之谨也。愚因是尤有所感于心也。文姜之恶已极。
二国之患。而子同之生。适当文姜居鲁之日。此圣人所以备录于经。是别嫌明微之意也。齐人之诗曰。展我甥兮。所以明为鲁公之子也。特书于经。亦犹齐诗之意也。圣人于删诗之际。所以存而不去。与鲁史之笔相为表里。其致谨于国储之生。至矣。惟后世昧于此义。故以吕易嬴而伯翳之祀忽诸。以牛易马而晋氏之宗乱真。可不谨哉。胡传谓适冢之生。即书于册(一作策)。与子之法也。经书子同生。所以明与子之法也。呜呼。此岂知圣人言外之旨乎。春秋之旨。果止于此乎。若止如胡氏之说。则圣人何以不书文公,子恶之生。而明与子之法乎。不书文公,子恶。而独书子同之生。则胡氏之说。可知其不然也。或曰。然则圣人不书文公,子恶之生。亦有说乎。曰有。此仲尼非徒不书之也。旧史必书之。而仲尼反削之也。何者。鲁之诸公。嫡子之生三也。庄,文与子恶是也。是皆正嫡之生而春秋一例书嫡子生。则夫人能之是不过史氏之凡例也后世何以知圣人别嫌明微之意也。必也削文公,子恶之生。而独书子同之生。然后有以启国人之问。而致后世之谨也。愚因是尤有所感于心也。文姜之恶已极。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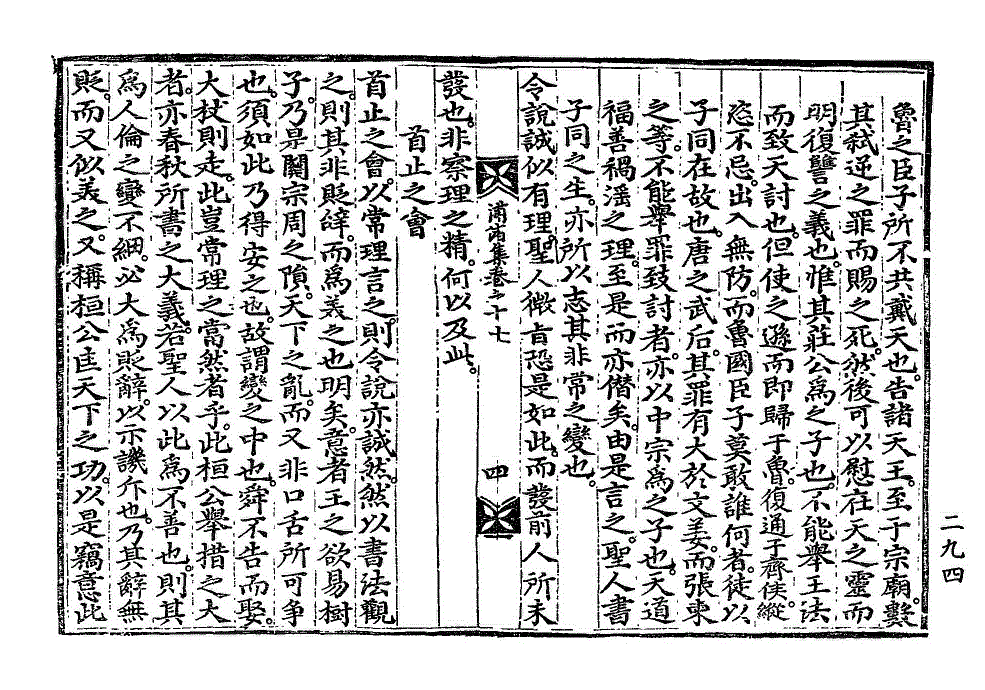 鲁之臣子所不共戴天也。告诸天王。至于宗庙。数其弑逆之罪而赐之死。然后可以慰在天之灵而明复雠之义也。惟其庄公为之子也。不能举王法而致天讨也。但使之逊而即归于鲁。复通于齐侯。纵恣不忌。出入无防。而鲁国臣子莫敢谁何者。徒以子同在故也。唐之武后。其罪有大于文姜。而张柬之等。不能举罪致讨者。亦以中宗为之子也。天道福善祸淫之理。至是而亦僭矣。由是言之。圣人书子同之生。亦所以志其非常之变也。
鲁之臣子所不共戴天也。告诸天王。至于宗庙。数其弑逆之罪而赐之死。然后可以慰在天之灵而明复雠之义也。惟其庄公为之子也。不能举王法而致天讨也。但使之逊而即归于鲁。复通于齐侯。纵恣不忌。出入无防。而鲁国臣子莫敢谁何者。徒以子同在故也。唐之武后。其罪有大于文姜。而张柬之等。不能举罪致讨者。亦以中宗为之子也。天道福善祸淫之理。至是而亦僭矣。由是言之。圣人书子同之生。亦所以志其非常之变也。令说诚似有理。圣人微旨恐是如此。而发前人所未发也。非察理之精。何以及此。
首止之会
首止之会。以常理言之。则令说亦诚然。然以书法观之。则其非贬辞。而为美之也明矣。意者王之欲易树子。乃是关宗周之陨。天下之乱。而又非口舌所可争也。须如此乃得安之也。故谓变之中也。舜不告而娶。大杖则走。此岂常理之当然者乎。此桓公举措之大者。亦春秋所书之大义。若圣人以此为不善也。则其为人伦之变不细。必大为贬辞。以示讥斥也。乃其辞无贬。而又似美之。又称桓公匡天下之功。以是窃意此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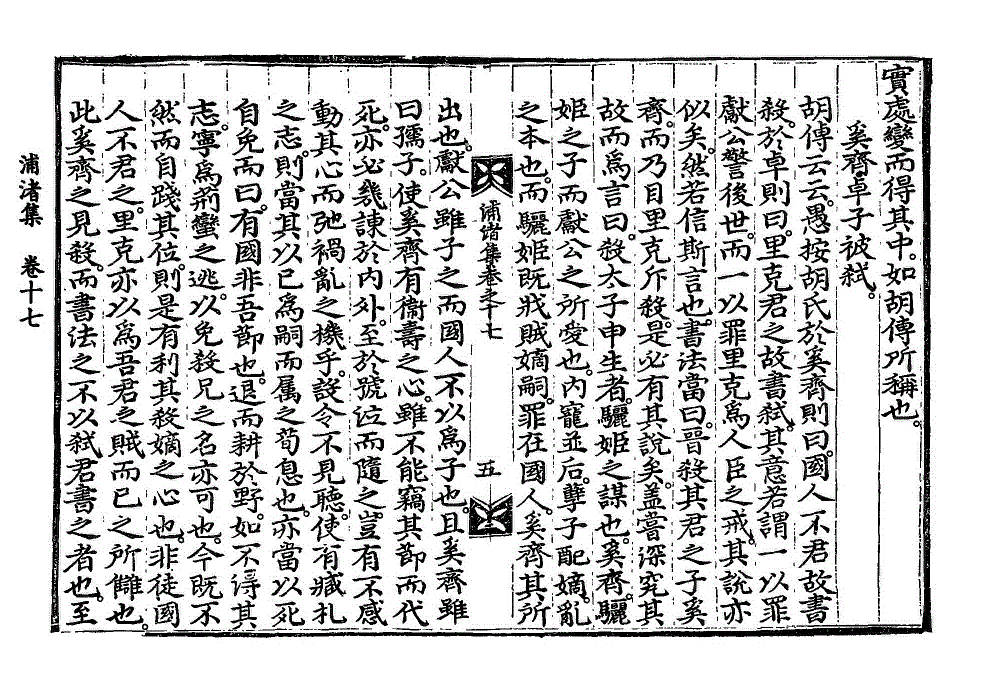 实处变而得其中。如胡传所称也。
实处变而得其中。如胡传所称也。奚齐,卓子被弑。
胡传云云。愚按胡氏于奚齐则曰。国人不君故书杀。于卓则曰。里克君之故书弑。其意若谓一以罪献公警后世。而一以罪里克为人臣之戒。其说亦似矣。然若信斯言也。书法当曰。晋杀其君之子奚齐。而乃目里克斥杀。是必有其说矣。盖尝深究其故而为言曰。杀太子申生者。骊姬之谋也。奚齐。骊姬之子而献公之所爱也。内宠并后。孽(一作嬖)子配嫡。乱之本也。而骊姬既戕贼嫡嗣。罪在国人。奚齐其所出也。献公虽子之而国人不以为子也。且奚齐虽曰孺子。使奚齐有卫寿之心。虽不能窃其节而代死。亦必几谏于内外。至于号泣而随之。岂有不感动其心而弛祸乱之机乎。设令不见听。使有臧札之志。则当其以己为嗣而属之荀息也。亦当以死自免而曰。有国非吾节也。退而耕于野。如不得其志。宁为荆蛮之逃。以免杀兄之名亦可也。今既不然而自践其位。则是有利其杀嫡之心也。非徒国人不君之。里克亦以为吾君之贼而己之所雠也。此奚齐之见杀。而书法之不以弑君书之者也。至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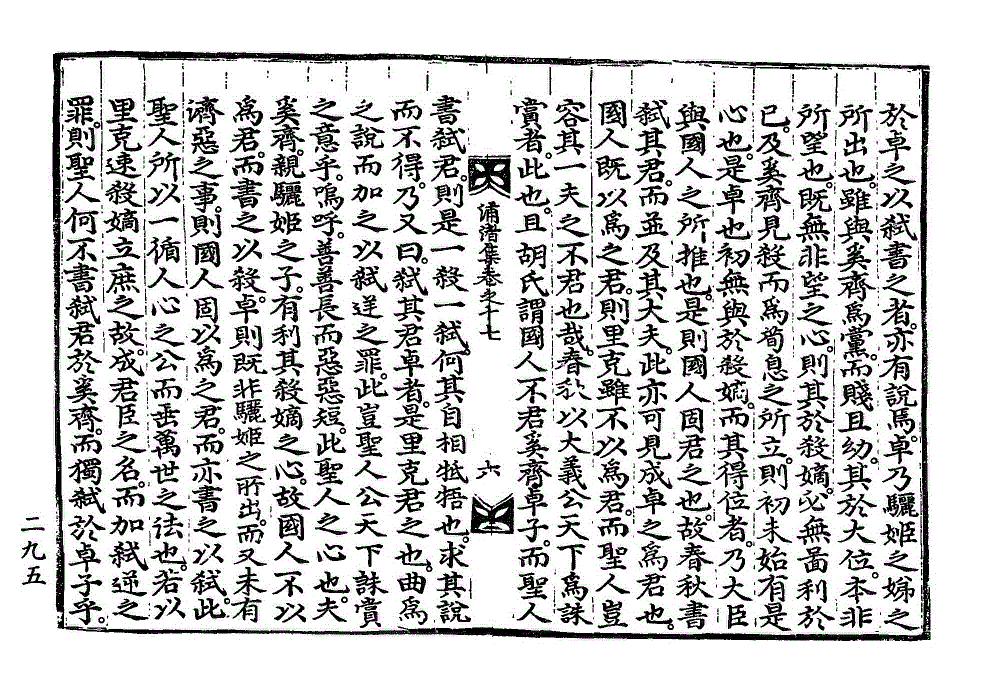 于卓之以弑书之者。亦有说焉。卓乃骊姬之娣之所出也。虽与奚齐为党。而贱且幼。其于大位。本非所望也。既无非望之心。则其于杀嫡。必无图利于己。及奚齐见杀而为荀息之所立。则初未始有是心也。是卓也初无与于杀嫡。而其得位者。乃大臣与国人之所推也。是则国人固君之也。故春秋书弑其君。而并及其大夫。此亦可见成卓之为君也。国人既以为之君。则里克虽不以为君。而圣人岂容其一夫之不君也哉。春秋以大义公天下为诛赏者。此也。且胡氏谓国人不君奚齐,卓子。而圣人书弑君。则是一杀一弑。何其自相牴牾也。求其说而不得。乃又曰。弑其君卓者。是里克君之也。曲为之说而加之以弑逆之罪。此岂圣人公天下诛赏之意乎。呜呼。善善长而恶恶短。此圣人之心也。夫奚齐。亲骊姬之子。有利其杀嫡之心。故国人不以为君。而书之以杀。卓则既非骊姬之所出。而又未有济恶之事。则国人固以为之君。而亦书之以弑。此圣人所以一循人心之公而垂万世之法也。若以里克速杀嫡立庶之故。成君臣之名。而加弑逆之罪。则圣人何不书弑君于奚齐。而独弑于卓子乎。
于卓之以弑书之者。亦有说焉。卓乃骊姬之娣之所出也。虽与奚齐为党。而贱且幼。其于大位。本非所望也。既无非望之心。则其于杀嫡。必无图利于己。及奚齐见杀而为荀息之所立。则初未始有是心也。是卓也初无与于杀嫡。而其得位者。乃大臣与国人之所推也。是则国人固君之也。故春秋书弑其君。而并及其大夫。此亦可见成卓之为君也。国人既以为之君。则里克虽不以为君。而圣人岂容其一夫之不君也哉。春秋以大义公天下为诛赏者。此也。且胡氏谓国人不君奚齐,卓子。而圣人书弑君。则是一杀一弑。何其自相牴牾也。求其说而不得。乃又曰。弑其君卓者。是里克君之也。曲为之说而加之以弑逆之罪。此岂圣人公天下诛赏之意乎。呜呼。善善长而恶恶短。此圣人之心也。夫奚齐。亲骊姬之子。有利其杀嫡之心。故国人不以为君。而书之以杀。卓则既非骊姬之所出。而又未有济恶之事。则国人固以为之君。而亦书之以弑。此圣人所以一循人心之公而垂万世之法也。若以里克速杀嫡立庶之故。成君臣之名。而加弑逆之罪。则圣人何不书弑君于奚齐。而独弑于卓子乎。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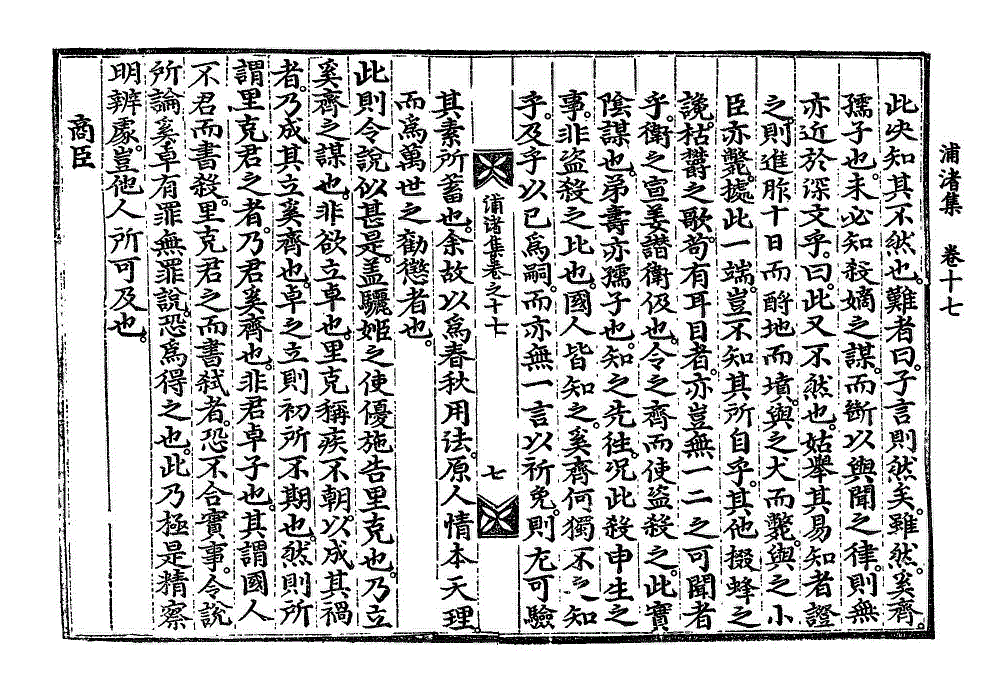 此决知其不然也。难者曰。子言则然矣。虽然。奚齐。孺子也。未必知杀嫡之谋。而断以与闻之律。则无亦近于深文乎。曰。此又不然也。姑举其易知者證之。则进胙十(一作六)日而酹地而坟。与之犬而毙。与之小臣亦毙。据此一端。岂不知其所自乎。其他掇蜂之谗。枯郁之歌。苟有耳目者。亦岂无一二之可闻者乎。卫之宣姜谮卫伋也。令之齐而使盗杀之。此实阴谋也。弟寿亦孺子也。知之先往。况此杀申生之事。非盗杀之比也。国人皆知之。奚齐何独不之知乎。及乎以己为嗣。而亦无一言以祈免。则尤可验其素所蓄也。余故以为春秋用法。原人情本天理。而为万世之劝惩者也。
此决知其不然也。难者曰。子言则然矣。虽然。奚齐。孺子也。未必知杀嫡之谋。而断以与闻之律。则无亦近于深文乎。曰。此又不然也。姑举其易知者證之。则进胙十(一作六)日而酹地而坟。与之犬而毙。与之小臣亦毙。据此一端。岂不知其所自乎。其他掇蜂之谗。枯郁之歌。苟有耳目者。亦岂无一二之可闻者乎。卫之宣姜谮卫伋也。令之齐而使盗杀之。此实阴谋也。弟寿亦孺子也。知之先往。况此杀申生之事。非盗杀之比也。国人皆知之。奚齐何独不之知乎。及乎以己为嗣。而亦无一言以祈免。则尤可验其素所蓄也。余故以为春秋用法。原人情本天理。而为万世之劝惩者也。此则令说似甚是。盖骊姬之使优施告里克也。乃立奚齐之谋也。非欲立卓也。里克称疾不朝。以成其祸者。乃成其立奚齐也。卓之立则初所不期也。然则所谓里克君之者。乃君奚齐也。非君卓子也。其谓国人不君而书杀。里克君之而书弑者。恐不合实事。令说所论奚,卓有罪无罪说。恐为得之也。此乃极是精察明辨处。岂他人所可及也。
商臣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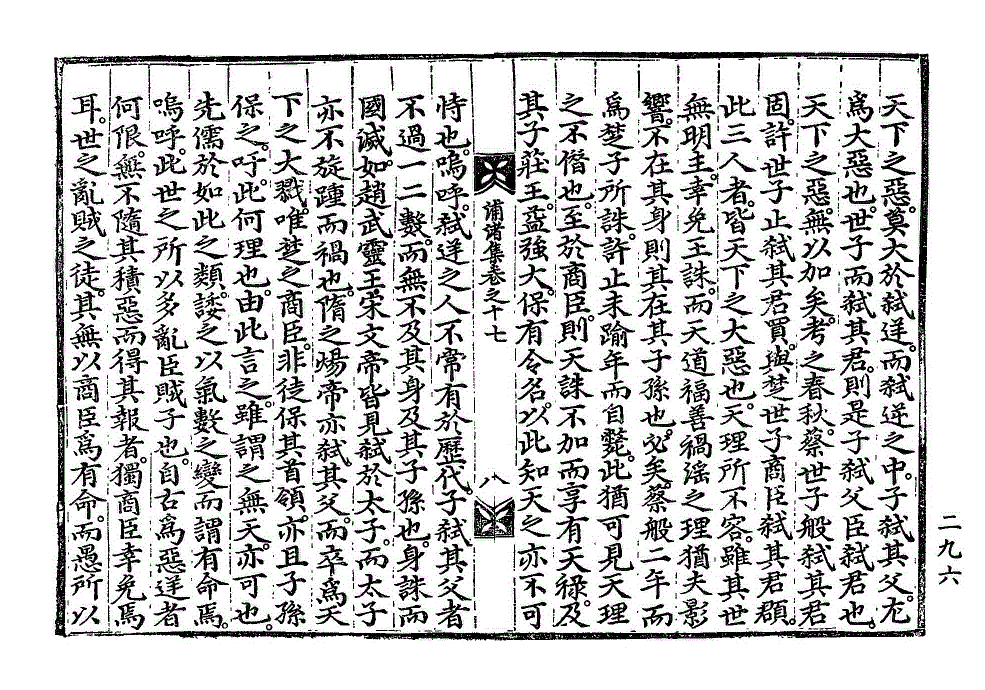 天下之恶。莫大于弑逆。而弑逆之中。子弑其父。尤为大恶也。世子而弑其君。则是子弑父臣弑君也。天下之恶。无以加矣。考之春秋。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此三人者。皆天下之大恶也。天理所不容。虽其世无明主。幸免王诛。而天道福善祸淫之理犹夫影响。不在其身则其在其子孙也。必矣。蔡般十(‘十’字를 보충해 넣었다.)二年而为楚子所诛。许止未踰年而自毙。此犹可见天理之不僭也。至于商臣。则天诛不加而享有天禄。及其子庄王。益强大。保有令名。以此知天之亦不可恃也。呜呼。弑逆之人不常有于历代。子弑其父者不过一二数。而无不及其身及其子孙也。身诛而国灭。如赵武灵王,宋文帝皆见弑于太子。而太子亦不旋踵而祸也。隋之炀帝亦弑其父。而卒为天下之大戮。唯楚之商臣。非徒保其首领。亦且子孙保之。吁。此何理也。由此言之。虽谓之无天。亦可也。先儒于如此之类。诿之以气数之变而谓有命焉。呜呼。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也。自右为恶逆者何限。无不随其积恶而得其报者。独商臣幸免焉耳。世之乱贼之徒。其无以商臣为有命。而愚所以
天下之恶。莫大于弑逆。而弑逆之中。子弑其父。尤为大恶也。世子而弑其君。则是子弑父臣弑君也。天下之恶。无以加矣。考之春秋。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此三人者。皆天下之大恶也。天理所不容。虽其世无明主。幸免王诛。而天道福善祸淫之理犹夫影响。不在其身则其在其子孙也。必矣。蔡般十(‘十’字를 보충해 넣었다.)二年而为楚子所诛。许止未踰年而自毙。此犹可见天理之不僭也。至于商臣。则天诛不加而享有天禄。及其子庄王。益强大。保有令名。以此知天之亦不可恃也。呜呼。弑逆之人不常有于历代。子弑其父者不过一二数。而无不及其身及其子孙也。身诛而国灭。如赵武灵王,宋文帝皆见弑于太子。而太子亦不旋踵而祸也。隋之炀帝亦弑其父。而卒为天下之大戮。唯楚之商臣。非徒保其首领。亦且子孙保之。吁。此何理也。由此言之。虽谓之无天。亦可也。先儒于如此之类。诿之以气数之变而谓有命焉。呜呼。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也。自右为恶逆者何限。无不随其积恶而得其报者。独商臣幸免焉耳。世之乱贼之徒。其无以商臣为有命。而愚所以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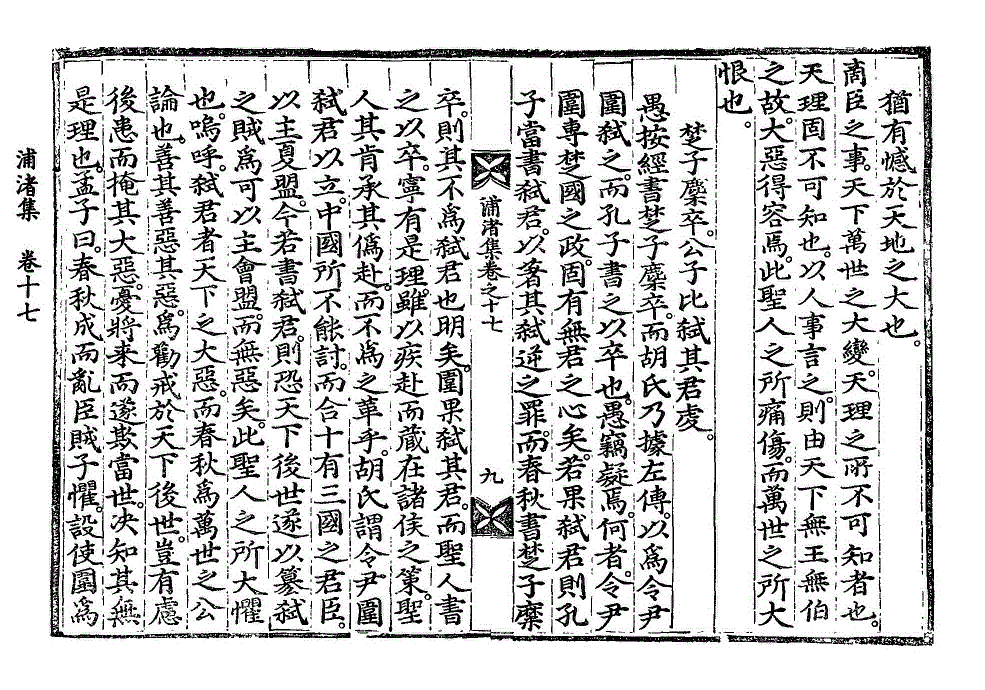 犹有憾于天地之大也。
犹有憾于天地之大也。商臣之事。天下万世之大变。天理之所不可知者也。天理固不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则由天下无王无伯之故。大恶得容焉。此圣人之所痛伤。而万世之所大恨也。
楚子麇卒。公子比弑其君处。
愚按经书楚子麇卒。而胡氏乃据左传。以为令尹围弑之。而孔子书之以卒也。愚窃疑焉。何者。令尹围专楚国之政。固有无君之心矣。若果弑君则孔子当书弑君。以著其弑逆之罪。而春秋书楚子糜卒。则其不为弑君也明矣。围果弑其君。而圣人书之以卒。宁有是理。虽以疾赴而藏在诸侯之策。圣人其肯承其伪赴。而不为之革乎。胡氏谓令尹围弑君以立。中国所不能讨。而合十有三国之君臣。以主夏盟。今若书弑君。则恐天下后世遂以篡弑之贼为可以主会盟。而无恶矣。此圣人之所大惧也。呜呼。弑君者天下之大恶。而春秋为万世之公论也。善其善恶其恶。为劝戒于天下后世。岂有虑后患而掩其大恶。忧将来而遂欺当世。决知其无是理也。孟子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设使围为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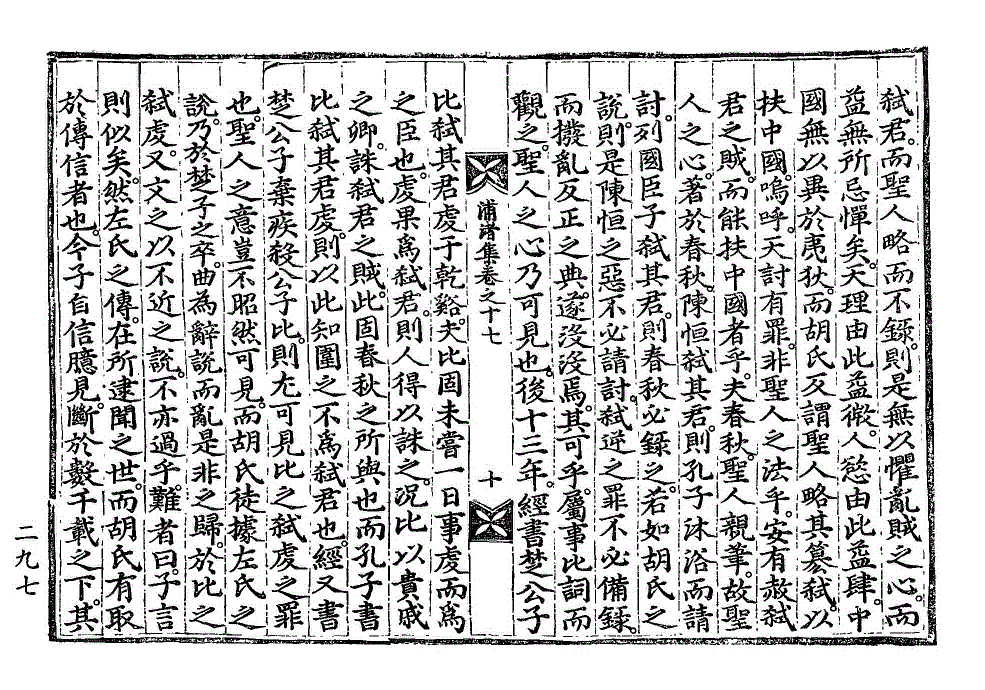 弑君。而圣人略而不录。则是无以惧乱贼之心。而益无所忌惮矣。天理由此益微。人欲由此益肆。中国无以异于夷狄。而胡氏反谓圣人略其篡弑。以扶中国。呜呼。天讨有罪。非圣人之法乎。安有赦弑君之贼。而能扶中国者乎。夫春秋。圣人亲笔。故圣人之心。著于春秋。陈恒弑其君。则孔子沐浴而请讨。列国臣子弑其君。则春秋必录之。若如胡氏之说。则是陈恒之恶不必请讨。弑逆之罪不必备录。而拨乱反正之典。遂没没焉。其可乎。属事比词而观之。圣人之心乃可见也。后十三年。经书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溪。夫比固未尝一日事虔而为之臣也。虔果为弑君。则人得以诛之。况比以贵戚之卿。诛弑君之贼。此固春秋之所与也而孔子书比弑其君虔。则以此知围之不为弑君也。经又书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则尤可见比之弑虔之罪也。圣人之意岂不昭然可见。而胡氏徒据左氏之说。乃于楚子之卒。曲为辞说而乱是非之归。于比之弑虔。又文之以不近之说。不亦过乎。难者曰。子言则似矣。然左氏之传。在所逮闻之世。而胡氏有取于传信者也。今子自信臆见。断于数千载之下。其
弑君。而圣人略而不录。则是无以惧乱贼之心。而益无所忌惮矣。天理由此益微。人欲由此益肆。中国无以异于夷狄。而胡氏反谓圣人略其篡弑。以扶中国。呜呼。天讨有罪。非圣人之法乎。安有赦弑君之贼。而能扶中国者乎。夫春秋。圣人亲笔。故圣人之心。著于春秋。陈恒弑其君。则孔子沐浴而请讨。列国臣子弑其君。则春秋必录之。若如胡氏之说。则是陈恒之恶不必请讨。弑逆之罪不必备录。而拨乱反正之典。遂没没焉。其可乎。属事比词而观之。圣人之心乃可见也。后十三年。经书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溪。夫比固未尝一日事虔而为之臣也。虔果为弑君。则人得以诛之。况比以贵戚之卿。诛弑君之贼。此固春秋之所与也而孔子书比弑其君虔。则以此知围之不为弑君也。经又书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则尤可见比之弑虔之罪也。圣人之意岂不昭然可见。而胡氏徒据左氏之说。乃于楚子之卒。曲为辞说而乱是非之归。于比之弑虔。又文之以不近之说。不亦过乎。难者曰。子言则似矣。然左氏之传。在所逮闻之世。而胡氏有取于传信者也。今子自信臆见。断于数千载之下。其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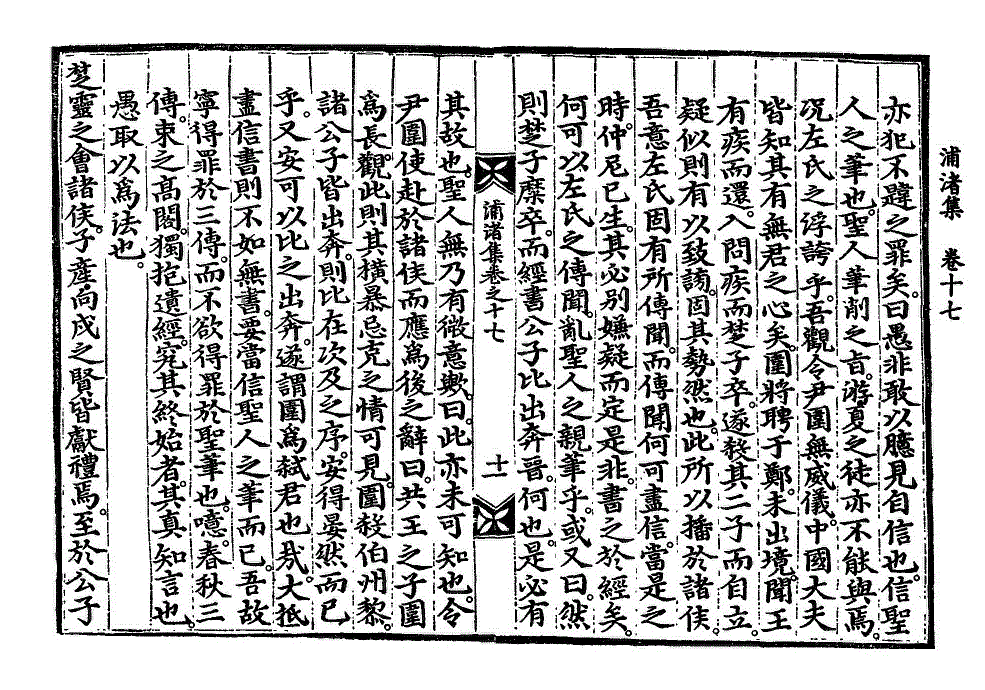 亦犯不韪之罪矣。曰愚非敢以臆见自信也。信圣人之笔也。圣人笔削之旨。游,夏之徒亦不能与焉。况左氏之浮誇乎。吾观令尹围无威仪。中国大夫皆知其有无君之心矣。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入问疾而楚子卒。遂杀其二子而自立。疑似则有以致谤。固其势然也。此所以播于诸侯。吾意左氏固有所传闻。而传闻何可尽信。当是之时。仲尼已生。其必别嫌疑而定是非。书之于经矣。何可以左氏之传闻。乱圣人之亲笔乎。或又曰。然则楚子糜(一作麇)卒。而经书公子比出奔晋。何也。是必有其故也。圣人无乃有微意欤。曰。此亦未可知也。令尹围使赴于诸侯而应为后之辞曰。共王之子围为长。观此则其横暴忌克之情可见。围杀伯州黎。诸公子皆出奔。则比在次及之序。安得晏然而已乎。又安可以比之出奔。遂谓围为弑君也哉。大抵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当信圣人之笔而已。吾故宁得罪于三传。而不欲得罪于圣笔也。噫。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抱遗经。究其终始者。其真知言也。愚取以为法也。
亦犯不韪之罪矣。曰愚非敢以臆见自信也。信圣人之笔也。圣人笔削之旨。游,夏之徒亦不能与焉。况左氏之浮誇乎。吾观令尹围无威仪。中国大夫皆知其有无君之心矣。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入问疾而楚子卒。遂杀其二子而自立。疑似则有以致谤。固其势然也。此所以播于诸侯。吾意左氏固有所传闻。而传闻何可尽信。当是之时。仲尼已生。其必别嫌疑而定是非。书之于经矣。何可以左氏之传闻。乱圣人之亲笔乎。或又曰。然则楚子糜(一作麇)卒。而经书公子比出奔晋。何也。是必有其故也。圣人无乃有微意欤。曰。此亦未可知也。令尹围使赴于诸侯而应为后之辞曰。共王之子围为长。观此则其横暴忌克之情可见。围杀伯州黎。诸公子皆出奔。则比在次及之序。安得晏然而已乎。又安可以比之出奔。遂谓围为弑君也哉。大抵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当信圣人之笔而已。吾故宁得罪于三传。而不欲得罪于圣笔也。噫。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抱遗经。究其终始者。其真知言也。愚取以为法也。楚灵之会诸侯。子产,向戍之贤皆献礼焉。至于公子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8L 页
 比。未尝一日臣虔。而书弑其君。每读之至此。尝不快于心。今见令说。若如此则实甚明快可喜。第史氏所记。亦不可尽以为不信。此亦不敢断定也。
比。未尝一日臣虔。而书弑其君。每读之至此。尝不快于心。今见令说。若如此则实甚明快可喜。第史氏所记。亦不可尽以为不信。此亦不敢断定也。齐桓晋文
圣人许桓公者。取一时之功也。孟子,董子斥之者。明其心术之不正也。盖以其功言之。则当时天下赖以正焉。圣人安得不许之。非但五伯。如四公子之有功于当时。亦如令所说也。然凡论人品。当以义理之正为主。总而论之则圣贤之道。纯于仁义。至正至粹。无一毫私意。五伯则诈力仁义相杂者也。而诈力为内。仁义为外。诈力为实。仁义为假。若纯于诈力而仁义灭尽者。乃夷狄也。禽兽也。若四君者。又伯者之下也。其于仁义。假亦不能。而犹以意气为尚。比之无意气者。亦稍胜也。观人与自处不同。若观人则凡有功于人者。皆当许之。况五伯之功乎。若自处则岂可不以仁义为志。而以五伯之诈力。四君之意气。为可慕乎。夫善利之间。毫釐有差。千里其谬。须深绝诈力而后可以有进于正道。孟子,董子之论。岂非粹然纯正。学者立心人君治世之规范乎。若以为义利可以双行。王伯可以并用。则虽使真能双行并用。其为人乍善乍恶。世道乍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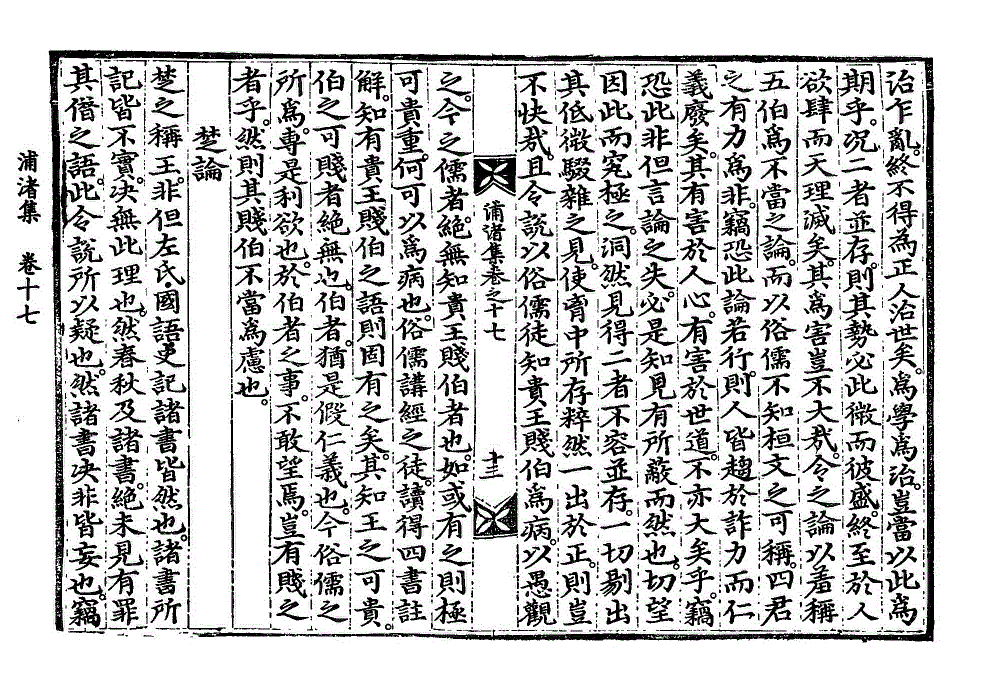 治乍乱。终不得为正人治世矣。为学为治。岂当以此为期乎。况二者并存。则其势必此微而彼盛。终至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其为害岂不大哉。令之论以羞称五伯为不当之论。而以俗儒不知桓文之可称。四君之有力为非。窃恐此论若行。则人皆趋于诈力而仁义废矣。其有害于人心。有害于世道。不亦大矣乎。窃恐此非但言论之失。必是知见有所蔽而然也。切望因此而究极之。洞然见得二者不容并存。一切剔出其低微䮕杂之见。使胸中所存粹然一出于正。则岂不快哉。且令说以俗儒徒知贵王贱伯为病。以愚观之。今之儒者。绝无知贵王贱伯者也。如或有之则极可贵重。何可以为病也。俗儒讲经之徒。读得四书注解。知有贵王贱伯之语则固有之矣。其知王之可贵。伯之可贱者绝无也。伯者。犹是假仁义也。今俗儒之所为。专是利欲也。于伯者之事。不敢望焉。岂有贱之者乎。然则其贱伯不当为虑也。
治乍乱。终不得为正人治世矣。为学为治。岂当以此为期乎。况二者并存。则其势必此微而彼盛。终至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其为害岂不大哉。令之论以羞称五伯为不当之论。而以俗儒不知桓文之可称。四君之有力为非。窃恐此论若行。则人皆趋于诈力而仁义废矣。其有害于人心。有害于世道。不亦大矣乎。窃恐此非但言论之失。必是知见有所蔽而然也。切望因此而究极之。洞然见得二者不容并存。一切剔出其低微䮕杂之见。使胸中所存粹然一出于正。则岂不快哉。且令说以俗儒徒知贵王贱伯为病。以愚观之。今之儒者。绝无知贵王贱伯者也。如或有之则极可贵重。何可以为病也。俗儒讲经之徒。读得四书注解。知有贵王贱伯之语则固有之矣。其知王之可贵。伯之可贱者绝无也。伯者。犹是假仁义也。今俗儒之所为。专是利欲也。于伯者之事。不敢望焉。岂有贱之者乎。然则其贱伯不当为虑也。楚论
楚之称王。非但左氏,国语,史记诸书皆然也。诸书所记皆不实。决无此理也。然春秋及诸书。绝未见有罪其僭之语。此令说所以疑也。然诸书决非皆妄也。窃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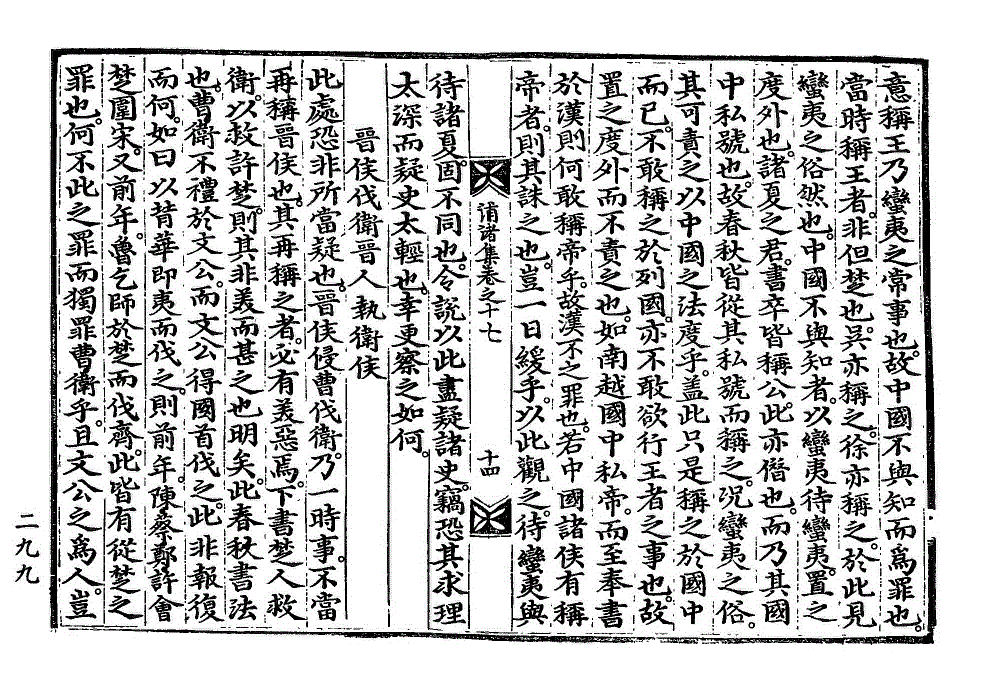 意称王乃蛮夷之常事也。故中国不与知而为罪也。当时称王者。非但楚也。吴亦称之。徐亦称之。于此见蛮夷之俗然也。中国不与知者。以蛮夷待蛮夷。置之度外也。诸夏之君。书卒皆称公。此亦僭也。而乃其国中私号也。故春秋皆从其私号而称之。况蛮夷之俗。其可责之以中国之法度乎。盖此只是称之于国中而已。不敢称之于列国。亦不敢欲行王者之事也。故置之度外而不责之也。如南越国中私帝。而至奉书于汉则何敢称帝乎。故汉不之罪也。若中国诸侯有称帝者。则其诛之也。岂一日缓乎。以此观之。待蛮夷与待诸夏。固不同也。令说以此尽疑诸史。窃恐其求理太深而疑史太轻也。幸更察之如何。
意称王乃蛮夷之常事也。故中国不与知而为罪也。当时称王者。非但楚也。吴亦称之。徐亦称之。于此见蛮夷之俗然也。中国不与知者。以蛮夷待蛮夷。置之度外也。诸夏之君。书卒皆称公。此亦僭也。而乃其国中私号也。故春秋皆从其私号而称之。况蛮夷之俗。其可责之以中国之法度乎。盖此只是称之于国中而已。不敢称之于列国。亦不敢欲行王者之事也。故置之度外而不责之也。如南越国中私帝。而至奉书于汉则何敢称帝乎。故汉不之罪也。若中国诸侯有称帝者。则其诛之也。岂一日缓乎。以此观之。待蛮夷与待诸夏。固不同也。令说以此尽疑诸史。窃恐其求理太深而疑史太轻也。幸更察之如何。晋使伐卫晋人执卫侯
此处恐非所当疑也。晋侯侵曹伐卫。乃一时事。不当再称晋侯也。其再称之者。必有美恶焉。下书楚人救卫。以救许楚。则其非美而甚之也明矣。此春秋书法也。曹,卫不礼于文公。而文公得国首伐之。此非报复而何。如曰以背华即夷而伐之。则前年。陈,蔡,郑,许会楚围宋。又前年。鲁乞师于楚而伐齐。此皆有从楚之罪也。何不此之罪而独罪曹,卫乎。且文公之为人。岂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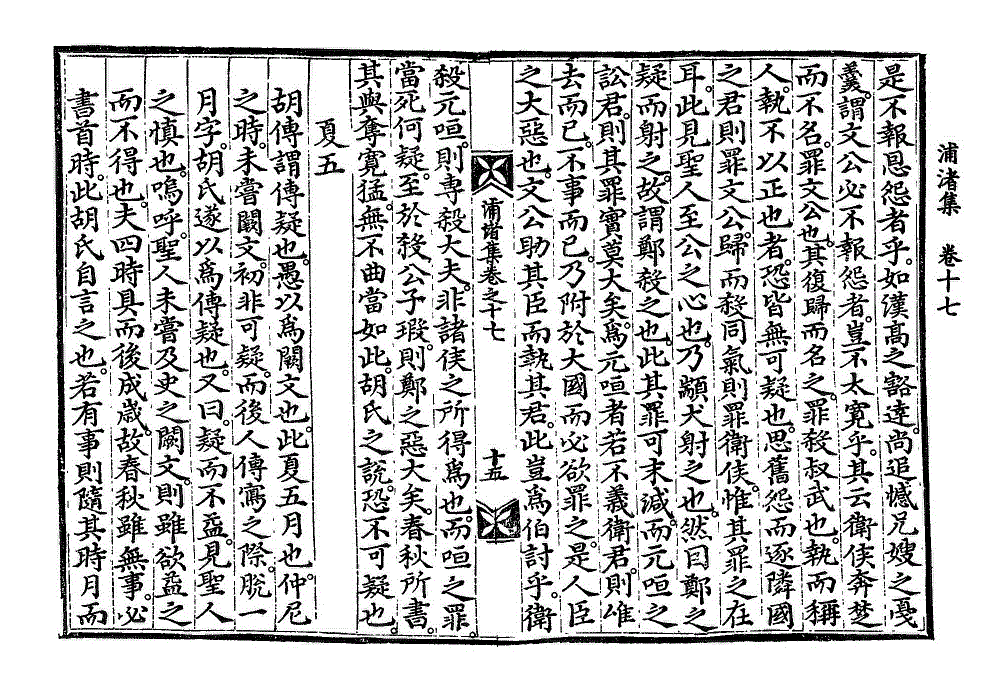 是不报恩怨者乎。如汉高之豁达。尚追憾兄嫂之戛羹。谓文公必不报怨者。岂不太宽乎。其云卫侯奔楚而不名。罪文公也。其复归而名之。罪杀叔武也。执而称人。执不以正也者。恐皆无可疑也。思旧怨而逐邻国之君则罪文公。归而杀同气则罪卫侯。惟其罪之在耳。此见圣人至公之心也。乃颛(一作歂)犬射之也。然因郑之疑而射之。故谓郑杀之也。此其罪可末减。而元咺之讼君。则其罪实莫大矣。为元咺者若不义卫君。则唯去而已。不事而已。乃附于大国而必欲罪之。是人臣之大恶也。文公助其臣而执其君。此岂为伯讨乎。卫杀元咺。则专杀大夫。非诸侯之所得为也。而咺之罪。当死何疑。至于杀公子瑕。则郑之恶大矣。春秋所书。其与夺宽猛。无不曲当如此。胡氏之说。恐不可疑也。
是不报恩怨者乎。如汉高之豁达。尚追憾兄嫂之戛羹。谓文公必不报怨者。岂不太宽乎。其云卫侯奔楚而不名。罪文公也。其复归而名之。罪杀叔武也。执而称人。执不以正也者。恐皆无可疑也。思旧怨而逐邻国之君则罪文公。归而杀同气则罪卫侯。惟其罪之在耳。此见圣人至公之心也。乃颛(一作歂)犬射之也。然因郑之疑而射之。故谓郑杀之也。此其罪可末减。而元咺之讼君。则其罪实莫大矣。为元咺者若不义卫君。则唯去而已。不事而已。乃附于大国而必欲罪之。是人臣之大恶也。文公助其臣而执其君。此岂为伯讨乎。卫杀元咺。则专杀大夫。非诸侯之所得为也。而咺之罪。当死何疑。至于杀公子瑕。则郑之恶大矣。春秋所书。其与夺宽猛。无不曲当如此。胡氏之说。恐不可疑也。夏五
胡传谓传疑也。愚以为阙文也。此夏五月也。仲尼之时。未尝阙文。初非可疑。而后人传写之际。脱一月字。胡氏遂以为传疑也。又曰。疑而不益。见圣人之慎也。呜呼。圣人未尝及史之阙文。则虽欲益之而不得也。夫四时具而后成岁。故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时。此胡氏自言之也。若有事则随其时月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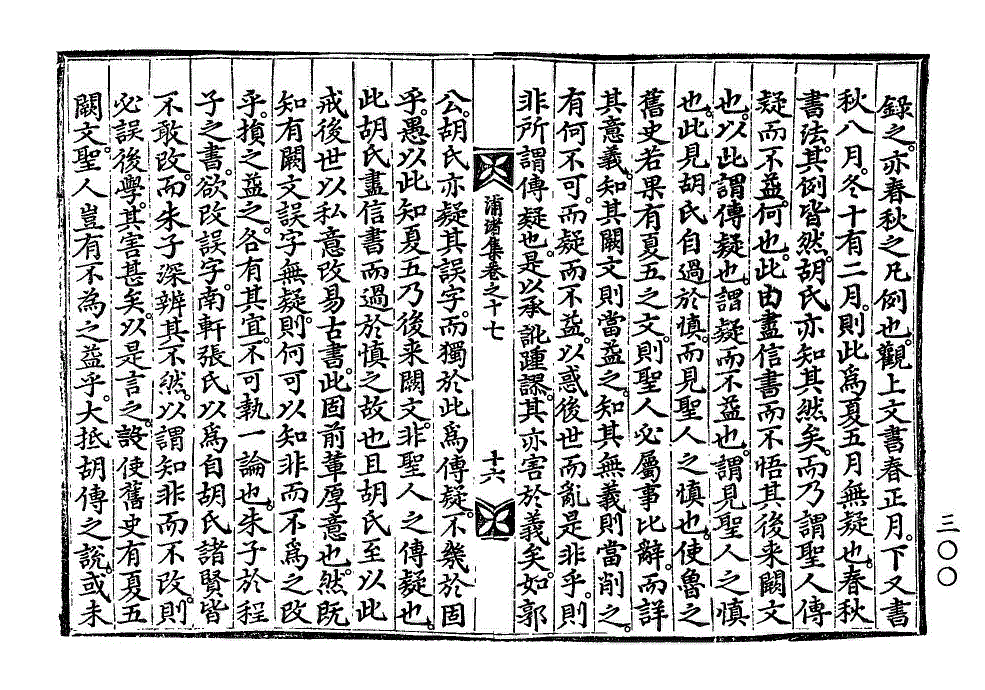 录之。亦春秋之凡例也。观上文书春正月。下又书秋八月。冬十有二月。则此为夏五月无疑也。春秋书法。其例皆然。胡氏亦知其然矣。而乃谓圣人传疑而不益。何也。此由尽信书而不悟其后来阙文也。以此谓传疑也。谓疑而不益也。谓见圣人之慎也。此见胡氏自过于慎。而见圣人之慎也。使鲁之旧史若果有夏五之文。则圣人必属事比辞。而详其意义。知其阙文则当益之。知其无义则当削之。有何不可。而疑而不益。以惑后世而乱是非乎。则非所谓传疑也。是以承讹踵谬。其亦害于义矣。如郭公。胡氏亦疑其误字。而独于此为传疑。不几于固乎。愚以此知夏五乃后来阙文。非圣人之传疑也。此胡氏尽信书而过于慎之故也。且胡氏至以此戒后世以私意改易古书。此固前辈厚意也。然既知有阙文误字无疑。则何可以知非而不为之改乎。损之益之。各有其宜。不可执一论也。朱子于程子之书。欲改误字。南轩张氏以为自胡氏诸贤皆不敢改。而朱子深辨其不然。以谓知非而不改。则必误后学。其害甚矣。以是言之。设使旧史有夏五阙文。圣人岂有不为之益乎。大抵胡传之说。或未
录之。亦春秋之凡例也。观上文书春正月。下又书秋八月。冬十有二月。则此为夏五月无疑也。春秋书法。其例皆然。胡氏亦知其然矣。而乃谓圣人传疑而不益。何也。此由尽信书而不悟其后来阙文也。以此谓传疑也。谓疑而不益也。谓见圣人之慎也。此见胡氏自过于慎。而见圣人之慎也。使鲁之旧史若果有夏五之文。则圣人必属事比辞。而详其意义。知其阙文则当益之。知其无义则当削之。有何不可。而疑而不益。以惑后世而乱是非乎。则非所谓传疑也。是以承讹踵谬。其亦害于义矣。如郭公。胡氏亦疑其误字。而独于此为传疑。不几于固乎。愚以此知夏五乃后来阙文。非圣人之传疑也。此胡氏尽信书而过于慎之故也。且胡氏至以此戒后世以私意改易古书。此固前辈厚意也。然既知有阙文误字无疑。则何可以知非而不为之改乎。损之益之。各有其宜。不可执一论也。朱子于程子之书。欲改误字。南轩张氏以为自胡氏诸贤皆不敢改。而朱子深辨其不然。以谓知非而不改。则必误后学。其害甚矣。以是言之。设使旧史有夏五阙文。圣人岂有不为之益乎。大抵胡传之说。或未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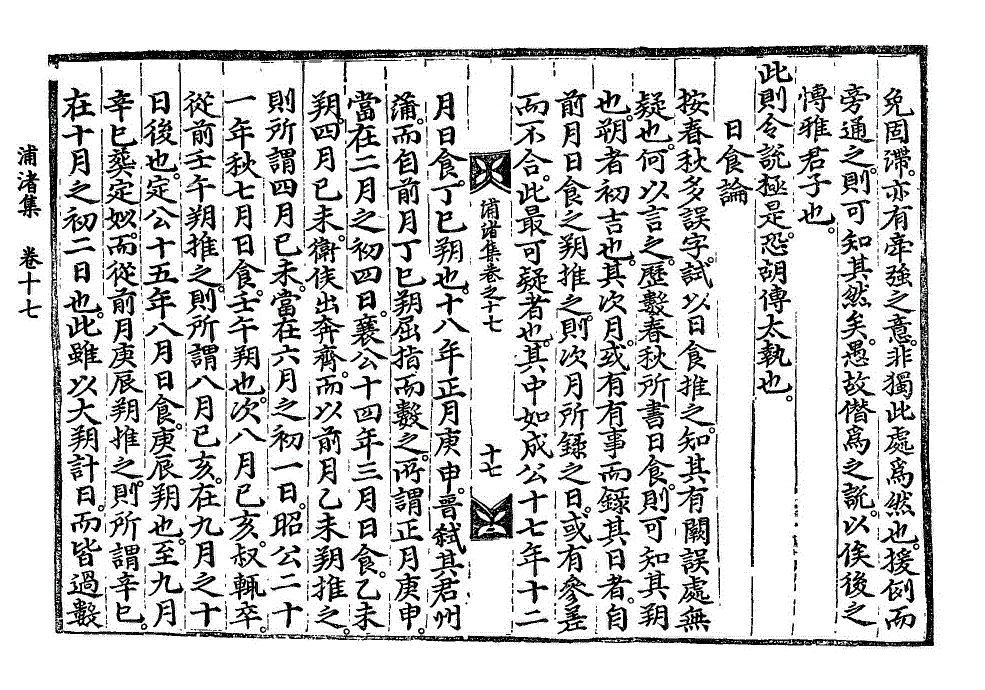 免固滞。亦有牵强之意。非独此处为然也。援例而旁通之。则可知其然矣。愚故僭为之说。以俟后之博雅君子也。
免固滞。亦有牵强之意。非独此处为然也。援例而旁通之。则可知其然矣。愚故僭为之说。以俟后之博雅君子也。此则令说极是。恐胡传太执也。
日食论
按春秋多误字。试以日食推之。知其有阙误处无疑也。何以言之。历数春秋所书日食。则可知其朔也。朔者初吉也。其次月。或有有事而录其日者。自前月日食之朔推之。则次月所录之日。或有参差而不合。此最可疑者也。其中如成公十七年十二月日食。丁巳朔也。十八年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而自前月丁巳朔屈指而数之。所谓正月庚申。当在二月之初四日。襄公十(衍字 十)四年三月日食。乙未朔。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而以前月乙未朔推之。则所谓四月己未。当在六月之初一日。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日食。壬午朔也。次八月己亥。叔辄卒。从前壬午朔推之。则所谓八月己亥。在九月之十日后也。定公十五年八月日食。庚辰朔也。至九月辛巳葬定姒。而从前月庚辰朔推之。则所谓辛巳。在十月之初二日也。此虽以大朔计日。而皆过数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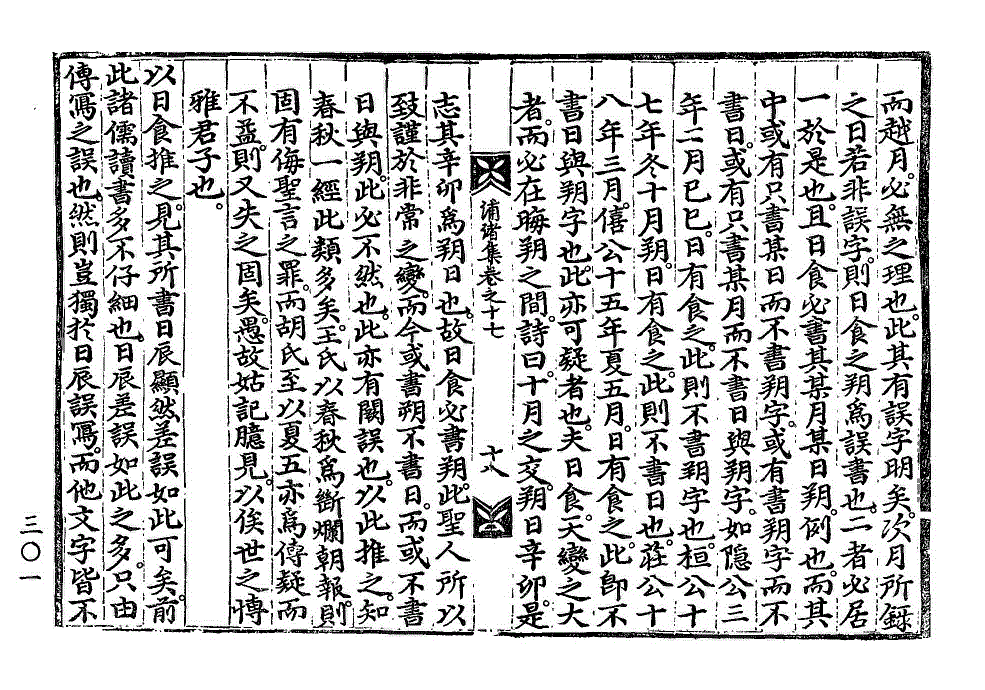 而越月。必无之理也。此其有误字明矣。次月所录之日若非误字。则日食之朔为误书也。二者必居一于是也。且日食必书其某月某日朔。例也。而其中或有只书某日而不书朔字。或有书朔字而不书日。或有只书某月而不书日与朔字。如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此则不书朔字也。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此则不书日也。庄公十八年三月。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此即不书日与朔字也。此亦可疑者也。夫日食。天变之大者。而必在晦朔之间。诗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志其辛卯为朔日也。故日食必书朔。此圣人所以致谨于非常之变。而今或书朔不书日。而或不书日与朔。此必不然也。此亦有阙误也。以此推之。知春秋一经此类多矣。王氏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则固有侮圣言之罪。而胡氏至以夏五亦为传疑而不益。则又失之固矣。愚故姑记臆见。以俟世之博雅君子也。
而越月。必无之理也。此其有误字明矣。次月所录之日若非误字。则日食之朔为误书也。二者必居一于是也。且日食必书其某月某日朔。例也。而其中或有只书某日而不书朔字。或有书朔字而不书日。或有只书某月而不书日与朔字。如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此则不书朔字也。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此则不书日也。庄公十八年三月。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此即不书日与朔字也。此亦可疑者也。夫日食。天变之大者。而必在晦朔之间。诗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志其辛卯为朔日也。故日食必书朔。此圣人所以致谨于非常之变。而今或书朔不书日。而或不书日与朔。此必不然也。此亦有阙误也。以此推之。知春秋一经此类多矣。王氏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则固有侮圣言之罪。而胡氏至以夏五亦为传疑而不益。则又失之固矣。愚故姑记臆见。以俟世之博雅君子也。以日食推之。见其所书日辰显然差误如此可矣。前此诸儒读书多不仔细也。日辰差误如此之多。只由传写之误也。然则岂独于日辰误写。而他文字皆不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2H 页
 误写也。其文既误写。则与初本异矣。其文既异。则其意自异矣。此所以多可疑处也。先儒到可疑处。不疑其误。而必强为之说。故其言多牵合。不合义理。此圣人所以贵阙疑也。能推索如是。知后人误写之多误说之多。则圣人笔削之旨。不为后人牵强之说所隐蔽。其有功于经文岂少哉。
误写也。其文既误写。则与初本异矣。其文既异。则其意自异矣。此所以多可疑处也。先儒到可疑处。不疑其误。而必强为之说。故其言多牵合。不合义理。此圣人所以贵阙疑也。能推索如是。知后人误写之多误说之多。则圣人笔削之旨。不为后人牵强之说所隐蔽。其有功于经文岂少哉。盟于召陵
桓公伐楚。只是仅得其辞服而已。非如孔明之伐雍开得其心服。故其后齮龁邻国犹尔也。盖伯者之功效。其浅如此。如使当时有王者。则必能讨其僭王跋扈之罪。或削或贬或诛或灭。量其罪之轻重而处之。何者。王者得天下之心服。天下皆父母之。故号令之行。信之如流。伯者之服人。非服其心。乃服其外。故其号令仅能纠合而已。其从不固。安能诛讨如志乎。齐桓之于楚。仅得辞服而不能大挫。乃力不及也。此王伯之分霄壤不侔处也。然使当时无桓公。则其猾夏之祸。不可量矣。其能使之惩戢。不敢大肆凭陵。天下受其赐。其功曷可少哉。此春秋所以许之也。胡传所谓几乎王者之事。言其不暴不骄近于王者耳。非谓真王者事也。如云贞观之治几于成,康。贞观之治。何敢望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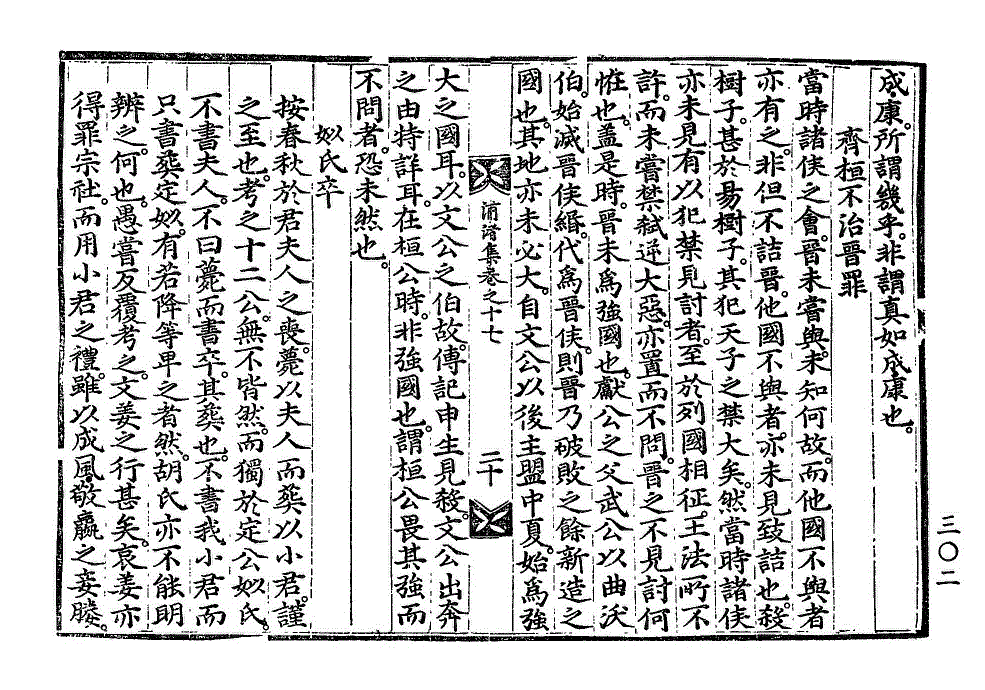 成,康。所谓几乎。非谓真如成,康也。
成,康。所谓几乎。非谓真如成,康也。齐桓不治晋罪
当时诸侯之会。晋未尝与。未知何故。而他国不与者亦有之。非但不诘晋。他国不与者。亦未见致诘也。杀树子。甚于易树子。其犯天子之禁大矣。然当时诸侯亦未见有以犯禁见讨者。至于列国相征。王法所不许。而未尝禁弑逆大恶。亦置而不问。晋之不见讨何怪也。盖是时。晋未为强国也。献公之父武公以曲沃伯。始灭晋侯缗。代为晋侯。则晋乃破败之馀新造之国也。其地亦未必大。自文公以后主盟中夏。始为强大之国耳。以文公之伯故。传记申生见杀。文公出奔之由特详耳。在桓公时。非强国也。谓桓公畏其强而不问者。恐未然也。
姒氏卒
按春秋于君夫人之丧。薨以夫人而葬以小君。谨之至也。考之十二公。无不皆然。而独于定公姒氏。不书夫人。不曰薨而书卒。其葬也。不书我小君而只书葬定姒。有若降等卑之者然。胡氏亦不能明辨之。何也。愚尝反覆考之。文姜之行甚矣。哀姜亦得罪宗社。而用小君之礼。虽以成风,敬嬴之妾媵。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3H 页
 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而无贬以正之。胡氏以为文姜既为国君之母。臣子致其送终之礼。不可得以贬也。又以成风,敬嬴则圣人纪禯之所由变。出于私情而非义。虽欲正之而不可。此无论其嫡妾之分善恶之殊。而用小君之典礼。同一例也。若定姒则不然。以先君之嫡体。为国君之生母。其分则夫人矣。其德则无非也。圣人何独于此变其常例。不书夫人小君而只书卒葬。有若降等示贬。左氏谓以不赴不祔。故不称夫人。此必无之理也。愚以此知春秋有阙误处多矣。此必有阙误无疑也。如春秋书葬蔡桓侯。胡氏以为蔡季之贤。知请谥也。而朱子以为只是文误。亦此类也。且隐公二年。书夫人子氏薨。胡氏以为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然朱子则言夫人子氏。只是仲子。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也。且三年夏四月辛卯。书尹氏卒。胡氏以为尹氏。天子大夫。家父所刺秉国不平者也。此则愚窃考于诗。时之先后。皆不可信。而必谓之讥世卿者固矣。历考于经。天子大夫。只王子虎,刘卷书卒而不录其日。虽以二公之贤。只书卒而不录日。则此乃略外之法也。今尹氏之
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而无贬以正之。胡氏以为文姜既为国君之母。臣子致其送终之礼。不可得以贬也。又以成风,敬嬴则圣人纪禯之所由变。出于私情而非义。虽欲正之而不可。此无论其嫡妾之分善恶之殊。而用小君之典礼。同一例也。若定姒则不然。以先君之嫡体。为国君之生母。其分则夫人矣。其德则无非也。圣人何独于此变其常例。不书夫人小君而只书卒葬。有若降等示贬。左氏谓以不赴不祔。故不称夫人。此必无之理也。愚以此知春秋有阙误处多矣。此必有阙误无疑也。如春秋书葬蔡桓侯。胡氏以为蔡季之贤。知请谥也。而朱子以为只是文误。亦此类也。且隐公二年。书夫人子氏薨。胡氏以为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然朱子则言夫人子氏。只是仲子。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也。且三年夏四月辛卯。书尹氏卒。胡氏以为尹氏。天子大夫。家父所刺秉国不平者也。此则愚窃考于诗。时之先后。皆不可信。而必谓之讥世卿者固矣。历考于经。天子大夫。只王子虎,刘卷书卒而不录其日。虽以二公之贤。只书卒而不录日。则此乃略外之法也。今尹氏之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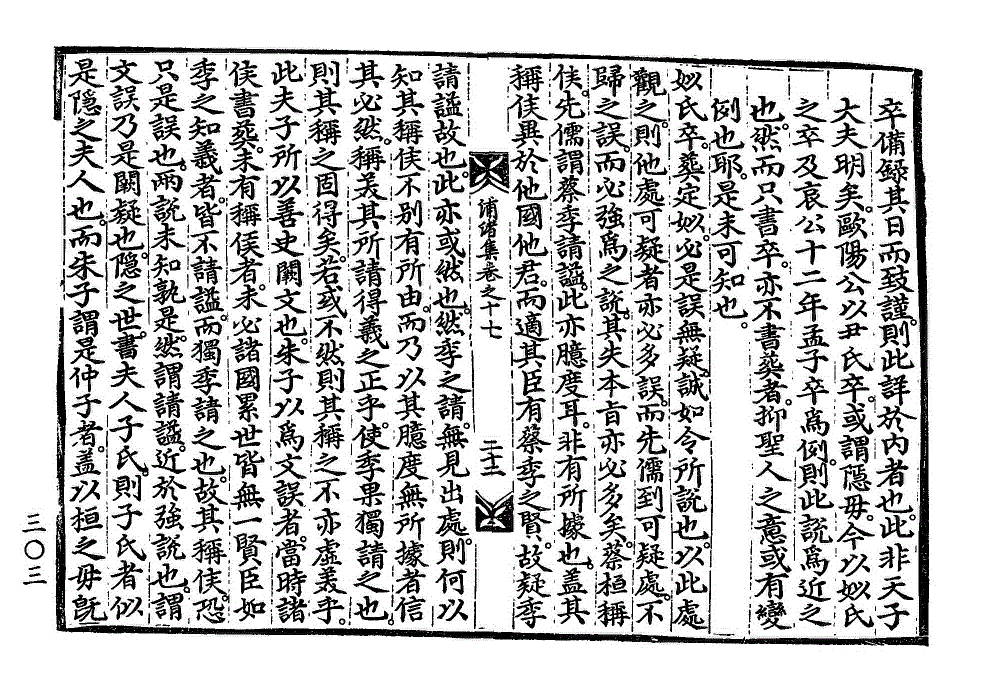 卒备录其日而致谨。则此详于内者也。此非天子大夫明矣。欧阳公以尹氏卒。或谓隐母。今以姒氏之卒及哀公十二年孟子卒为例。则此说为近之也。然而只书卒。亦不书葬者。抑圣人之意或有变例也耶。是未可知也。
卒备录其日而致谨。则此详于内者也。此非天子大夫明矣。欧阳公以尹氏卒。或谓隐母。今以姒氏之卒及哀公十二年孟子卒为例。则此说为近之也。然而只书卒。亦不书葬者。抑圣人之意或有变例也耶。是未可知也。姒氏卒。葬定姒。必是误无疑。诚如令所说也。以此处观之。则他处可疑者亦必多误。而先儒到可疑处。不归之误。而必强为之说。其失本旨亦必多矣。蔡桓称侯。先儒谓蔡季请谥。此亦臆度耳。非有所据也。盖其称侯异于他国他君。而适其臣有蔡季之贤。故疑季请谥故也。此亦或然也。然季之请。无见出处。则何以知其称侯不别有所由。而乃以其臆度无所据者信其必然。称美其所请得义之正乎。使季果独请之也。则其称之固得矣。若或不然则其称之不亦虚美乎。此夫子所以善史阙文也。朱子以为文误者。当时诸侯书葬。未有称侯者。未必诸国累世皆无一贤臣如季之知义者。皆不请谥。而独季请之也。故其称侯。恐只是误也。两说未知孰是。然谓请谥。近于强说也。谓文误乃是阙疑也。隐之世。书夫人子氏。则子氏者似是隐之夫人也。而朱子谓是仲子者。盖以桓之母既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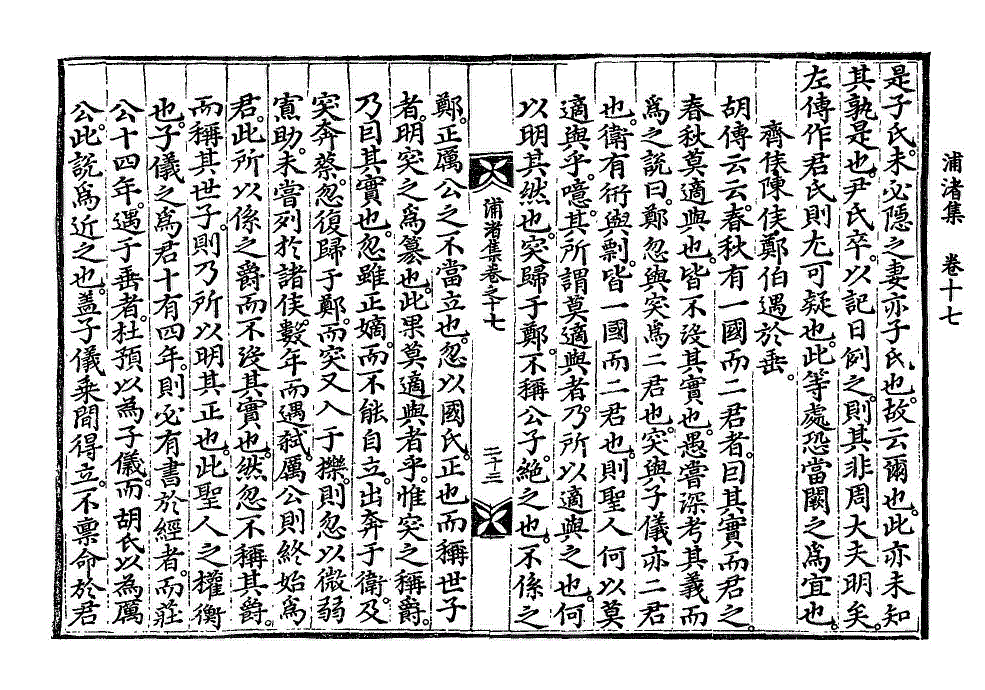 是子氏。未必隐之妻亦子氏也。故云尔也。此亦未知其孰是也。尹氏卒。以记日例之。则其非周大夫明矣。左传作君氏则尤可疑也。此等处恐当阙之为宜也。
是子氏。未必隐之妻亦子氏也。故云尔也。此亦未知其孰是也。尹氏卒。以记日例之。则其非周大夫明矣。左传作君氏则尤可疑也。此等处恐当阙之为宜也。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胡传云云。春秋有一国而二君者。因其实而君之。春秋莫适与也。皆不没其实也。愚尝深考其义而为之说曰。郑忽与突为二君也。突与子仪亦二君也。卫有衎与剽。皆一国而二君也。则圣人何以莫适与乎。噫。其所谓莫适与者。乃所以适与之也。何以明其然也。突归于郑。不称公子。绝之也。不系之郑。正厉公之不当立也。忽以国氏。正也而称世子者。明突之为篡也。此果莫适与者乎。惟突之称爵。乃因其实也。忽虽正嫡。而不能自立。出奔于卫。及突奔蔡。忽复归于郑。而突又入于栎。则忽以微弱寡助。未尝列于诸侯。数年而遇弑。厉公则终始为君。此所以系之爵而不没其实也。然忽不称其爵。而称其世子。则乃所以明其正也。此圣人之权衡也。子仪之为君十有四年。则必有书于经者。而庄公十四年。遇于垂者。杜预以为子仪。而胡氏以为厉公。此说为近之也。盖子仪乘间得之。不禀命于君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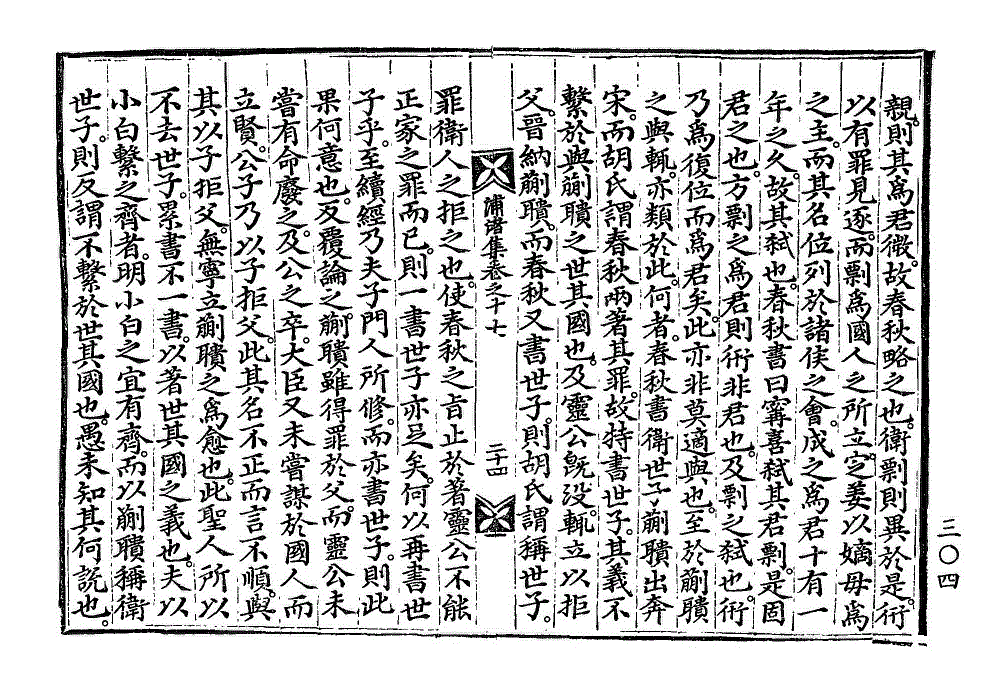 亲。则其为君微。故春秋略之也。卫剽则异于是。衎以有罪见逐。而剽为国人之所立。定姜以嫡母为之主。而其名位列于诸侯之会。成之为君十有一年之久。故其弑也。春秋书曰宁喜弑其君剽。是固君之也。方剽之为君则衎非君也。及剽之弑也。衎乃为复位而为君矣。此亦非莫适与也。至于蒯聩之与辄。亦类于此。何者。春秋书卫世子蒯聩出奔宋。而胡氏谓春秋两著其罪。故特书世子。其义不系于与蒯聩之世其国也。及灵公既没。辄立以拒父。晋纳蒯聩。而春秋又书世子。则胡氏谓称世子。罪卫人之拒之也。使春秋之旨止于著灵公不能正家之罪而已。则一书世子亦足矣。何以再书世子乎。至续经乃夫子门人所修。而亦书世子。则此果何意也。反覆论之。蒯聩虽得罪于父。而灵公未尝有命废之。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尝谋于国人而立贤。公子乃以子拒父。此其名不正而言不顺。与其以子拒父。无宁立蒯聩之为愈也。此圣人所以不去世子。累书不一书。以著世其国之义也。夫以小白系之齐者。明小白之宜有齐。而以蒯聩称卫世子。则反谓不系于世其国也。愚未知其何说也。
亲。则其为君微。故春秋略之也。卫剽则异于是。衎以有罪见逐。而剽为国人之所立。定姜以嫡母为之主。而其名位列于诸侯之会。成之为君十有一年之久。故其弑也。春秋书曰宁喜弑其君剽。是固君之也。方剽之为君则衎非君也。及剽之弑也。衎乃为复位而为君矣。此亦非莫适与也。至于蒯聩之与辄。亦类于此。何者。春秋书卫世子蒯聩出奔宋。而胡氏谓春秋两著其罪。故特书世子。其义不系于与蒯聩之世其国也。及灵公既没。辄立以拒父。晋纳蒯聩。而春秋又书世子。则胡氏谓称世子。罪卫人之拒之也。使春秋之旨止于著灵公不能正家之罪而已。则一书世子亦足矣。何以再书世子乎。至续经乃夫子门人所修。而亦书世子。则此果何意也。反覆论之。蒯聩虽得罪于父。而灵公未尝有命废之。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尝谋于国人而立贤。公子乃以子拒父。此其名不正而言不顺。与其以子拒父。无宁立蒯聩之为愈也。此圣人所以不去世子。累书不一书。以著世其国之义也。夫以小白系之齐者。明小白之宜有齐。而以蒯聩称卫世子。则反谓不系于世其国也。愚未知其何说也。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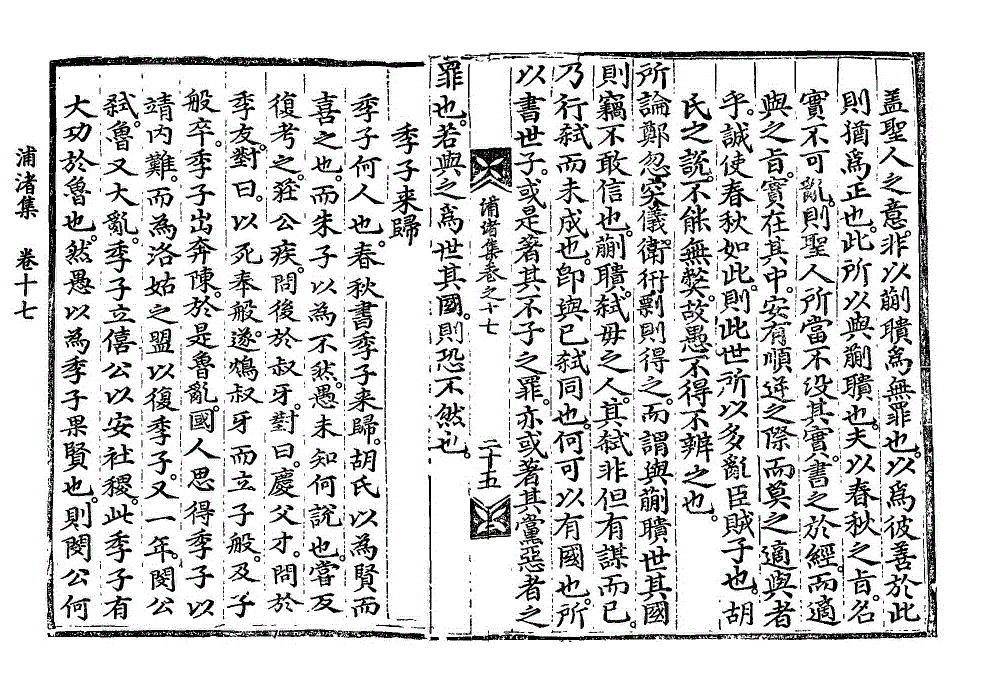 盖圣人之意。非以蒯聩为无罪也。以为彼善于此则犹为正也。此所以与蒯聩也。夫以春秋之旨。名实不可乱。则圣人所当不没其实。书之于经。而适与之旨。实在其中。安有顺逆之际而莫之适与者乎。诚使春秋如此。则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也。胡氏之说。不能无弊。故愚不得不辨之也。
盖圣人之意。非以蒯聩为无罪也。以为彼善于此则犹为正也。此所以与蒯聩也。夫以春秋之旨。名实不可乱。则圣人所当不没其实。书之于经。而适与之旨。实在其中。安有顺逆之际而莫之适与者乎。诚使春秋如此。则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也。胡氏之说。不能无弊。故愚不得不辨之也。所论郑忽,突,仪。卫衎,剽则得之。而谓与蒯聩世其国则窃不敢信也。蒯聩。弑母之人。其弑非但有谋而已。乃行弑而未成也。即与己弑同也。何可以有国也。所以书世子。或是著其不子之罪。亦或著其党恶者之罪也。若与之为世其国。则恐不然也。
季子来归
季子何人也。春秋书季子来归。胡氏以为贤而喜之也。而朱子以为不然。愚未知何说也。尝反复考之。庄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才。问于季友。对曰。以死奉般。遂鸩叔牙而立子般。及子般卒。季子出奔陈。于是鲁乱。国人思得季子以靖内难。而为洛姑之盟以复季子。又一年。闵公弑。鲁又大乱。季子立僖公以安社稷。此季子有大功于鲁也。然愚以为季子果贤也。则闵公何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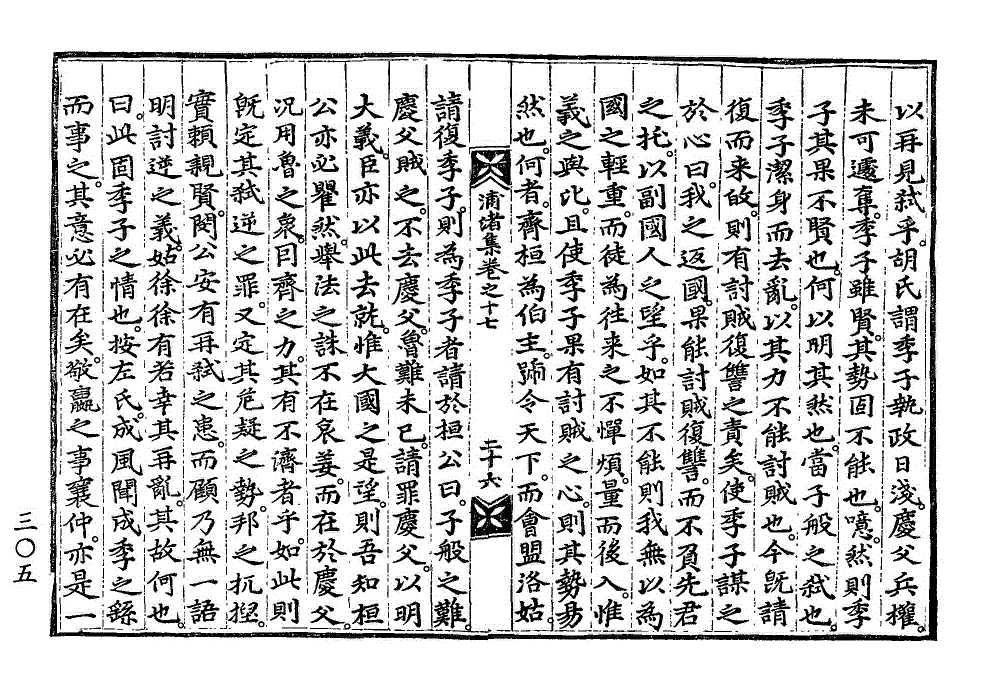 以再见弑乎。胡氏谓季子执政日浅。庆父兵权。未可遽夺。季子虽贤。其势固不能也。噫。然则季子其果不贤也。何以明其然也。当子般之弑也。季子洁身而去乱。以其力不能讨贼也。今既请复而来归。则有讨贼复雠之责矣。使季子谋之于心曰。我之返国。果能讨贼复雠。而不负先君之托。以副国人之望乎。如其不能则我无以为国之轻重。而徒为往来之不惮烦。量而后入。惟义之与比。且使季子果有讨贼之心。则其势易然也。何者。齐桓为伯主。号令天下。而会盟洛姑。请复季子。则为季子者请于桓公曰。子般之难。庆父贼之。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请罪庆父。以明大义。臣亦以此去就。惟大国之是望。则吾知桓公亦必瞿然。举法之诛不在哀姜。而在于庆父。况用鲁之众。因齐之力。其有不济者乎。如此则既定其弑逆之罪。又定其危疑之势。邦之扤捏。实赖亲贤。闵公安有再弑之患。而顾乃无一语明讨逆之义。姑徐徐有若幸其再乱。其故何也。曰。此固季子之情也。按左氏。成风闻成季之繇而事之。其意必有在矣。敬嬴之事襄仲。亦是一
以再见弑乎。胡氏谓季子执政日浅。庆父兵权。未可遽夺。季子虽贤。其势固不能也。噫。然则季子其果不贤也。何以明其然也。当子般之弑也。季子洁身而去乱。以其力不能讨贼也。今既请复而来归。则有讨贼复雠之责矣。使季子谋之于心曰。我之返国。果能讨贼复雠。而不负先君之托。以副国人之望乎。如其不能则我无以为国之轻重。而徒为往来之不惮烦。量而后入。惟义之与比。且使季子果有讨贼之心。则其势易然也。何者。齐桓为伯主。号令天下。而会盟洛姑。请复季子。则为季子者请于桓公曰。子般之难。庆父贼之。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请罪庆父。以明大义。臣亦以此去就。惟大国之是望。则吾知桓公亦必瞿然。举法之诛不在哀姜。而在于庆父。况用鲁之众。因齐之力。其有不济者乎。如此则既定其弑逆之罪。又定其危疑之势。邦之扤捏。实赖亲贤。闵公安有再弑之患。而顾乃无一语明讨逆之义。姑徐徐有若幸其再乱。其故何也。曰。此固季子之情也。按左氏。成风闻成季之繇而事之。其意必有在矣。敬嬴之事襄仲。亦是一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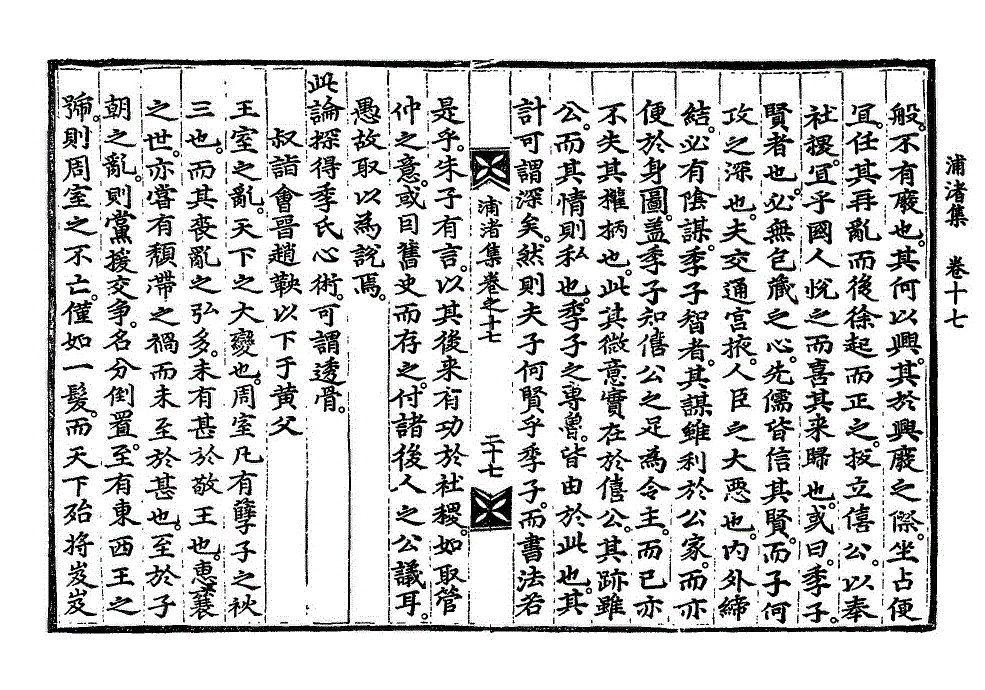 般。不有废也。其何以兴。其于兴废之际。坐占便宜。任其再乱而后徐起而正之。扳立僖公。以奉社稷。宜乎国人悦之而喜其来归也。或曰。季子。贤者也。必无包藏之心。先儒皆信其贤。而子何攻之深也。夫交通宫掖。人臣之大恶也。内外缔结。必有阴谋。季子智者。其谋虽利于公家。而亦便于身图。盖季子知僖公之足为令主。而己亦不失其权柄也。此其微意实在于僖公。其迹虽公。而其情则私也。季子之专鲁。皆由于此也。其计可谓深矣。然则夫子何贤乎季子。而书法若是乎。朱子有言。以其后来有功于社稷。如取管仲之意。或因旧史而存之。付诸后人之公议耳。愚故取以为说焉。
般。不有废也。其何以兴。其于兴废之际。坐占便宜。任其再乱而后徐起而正之。扳立僖公。以奉社稷。宜乎国人悦之而喜其来归也。或曰。季子。贤者也。必无包藏之心。先儒皆信其贤。而子何攻之深也。夫交通宫掖。人臣之大恶也。内外缔结。必有阴谋。季子智者。其谋虽利于公家。而亦便于身图。盖季子知僖公之足为令主。而己亦不失其权柄也。此其微意实在于僖公。其迹虽公。而其情则私也。季子之专鲁。皆由于此也。其计可谓深矣。然则夫子何贤乎季子。而书法若是乎。朱子有言。以其后来有功于社稷。如取管仲之意。或因旧史而存之。付诸后人之公议耳。愚故取以为说焉。此论探得季氏心术。可谓透骨。
叔诣会晋赵鞅以下于黄父
王室之乱。天下之大变也。周室凡有孽子之秋(一作祸)三也。而其丧乱之弘多。未有甚于敬王也。惠,襄之世。亦尝有颓带之祸而未至于甚也。至于子朝之乱。则党援交争。名分倒置。至有东西王之号。则周室之不亡。仅如一发。而天下殆将岌岌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6L 页
 矣。于此之时。诸侯有能纠合义旅。翼戴王室。使不坠其宗祧。则桓文之绩。无以加焉。晋人乃能徵会于诸侯。以谋王室。而成纳王之功。则五伯之盛。未之有也。齐桓会诸侯于首止。以定王世子之位。则胡氏以为一匡天下。在于此举。故圣人美之。而今此黄父之会。则胡氏以为王室之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厥职。非异人任免于讥贬足矣。故春秋无美辞。此春秋以正待人之体也。呜呼。此果圣人之意乎。盖尝反复考之。而后可知其不然也。何者。按昭公二十二年夏。天王崩而王室乱。刘,单二子以王猛居于皇。秋。二子以王猛入居于王城。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五年夏。叔诣会晋赵鞅及八国之大夫于黄父。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而王子朝出奔。终于佚贼。则天下之诸侯。果能尽勤王之义。而为方伯者亦不无纵贼之罪也。自王室之乱。至子朝出奔。凡五年矣。其间周之畿内。干戈日争。生民糜乱。肝脑涂地。天王播越迁次。未有攸底。祸乱之惨。有不可言。而方伯连帅。未闻有奔走而赴乱。至范献子闻子大叔之
矣。于此之时。诸侯有能纠合义旅。翼戴王室。使不坠其宗祧。则桓文之绩。无以加焉。晋人乃能徵会于诸侯。以谋王室。而成纳王之功。则五伯之盛。未之有也。齐桓会诸侯于首止。以定王世子之位。则胡氏以为一匡天下。在于此举。故圣人美之。而今此黄父之会。则胡氏以为王室之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厥职。非异人任免于讥贬足矣。故春秋无美辞。此春秋以正待人之体也。呜呼。此果圣人之意乎。盖尝反复考之。而后可知其不然也。何者。按昭公二十二年夏。天王崩而王室乱。刘,单二子以王猛居于皇。秋。二子以王猛入居于王城。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五年夏。叔诣会晋赵鞅及八国之大夫于黄父。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而王子朝出奔。终于佚贼。则天下之诸侯。果能尽勤王之义。而为方伯者亦不无纵贼之罪也。自王室之乱。至子朝出奔。凡五年矣。其间周之畿内。干戈日争。生民糜乱。肝脑涂地。天王播越迁次。未有攸底。祸乱之惨。有不可言。而方伯连帅。未闻有奔走而赴乱。至范献子闻子大叔之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7H 页
 言。于是乎献子惧。乃与宣子图之。乃徵会于诸侯。期以明年黄父之会。又至明年之夏。单子如晋告急。然后晋人始至。帅师纳王。由是言之。此果克修厥职。不负方伯之责耶。向使子大叔不言于献子。单子不告其急。则吾知晋师之出。亦未可期也。晋人尝帅九州之戎。以纳王于王城。则亦非不知其邪正之分。而乃使士景伯莅问于周。问于介众。而后乃辞王子朝。则可知其有观望之意也。惟其舆言可畏。其势有不可已。乃始举义。故至于五年之后。仅能克之。而卒使子朝奉周之典籍。自逸于荆蛮。则此晋之罪也。为晋计者。当其乱始。即使问其乱故。而纠合诸侯。亲自释位以图其乱。则乱庶遄已。如此则可谓用力于王室。克修其职者也。顾乃疑于与王。缓于讨逆。迁延岁月。不自赴会。乃使其身(一作臣)会诸侯之大夫。而又不为纠合之盟。其视齐桓首止之会。轻重何如哉。此春秋之书法所以无美辞也。其意若曰。惟其纳王。仅可以赎罪而止也。胡氏所谓以正待人者。不亦颠乎。圣人盖于此。取其功而诛其意。因其事而不没其实。则亦安知圣人不使后之观者知其有讥贬之意也。若以其修厥
言。于是乎献子惧。乃与宣子图之。乃徵会于诸侯。期以明年黄父之会。又至明年之夏。单子如晋告急。然后晋人始至。帅师纳王。由是言之。此果克修厥职。不负方伯之责耶。向使子大叔不言于献子。单子不告其急。则吾知晋师之出。亦未可期也。晋人尝帅九州之戎。以纳王于王城。则亦非不知其邪正之分。而乃使士景伯莅问于周。问于介众。而后乃辞王子朝。则可知其有观望之意也。惟其舆言可畏。其势有不可已。乃始举义。故至于五年之后。仅能克之。而卒使子朝奉周之典籍。自逸于荆蛮。则此晋之罪也。为晋计者。当其乱始。即使问其乱故。而纠合诸侯。亲自释位以图其乱。则乱庶遄已。如此则可谓用力于王室。克修其职者也。顾乃疑于与王。缓于讨逆。迁延岁月。不自赴会。乃使其身(一作臣)会诸侯之大夫。而又不为纠合之盟。其视齐桓首止之会。轻重何如哉。此春秋之书法所以无美辞也。其意若曰。惟其纳王。仅可以赎罪而止也。胡氏所谓以正待人者。不亦颠乎。圣人盖于此。取其功而诛其意。因其事而不没其实。则亦安知圣人不使后之观者知其有讥贬之意也。若以其修厥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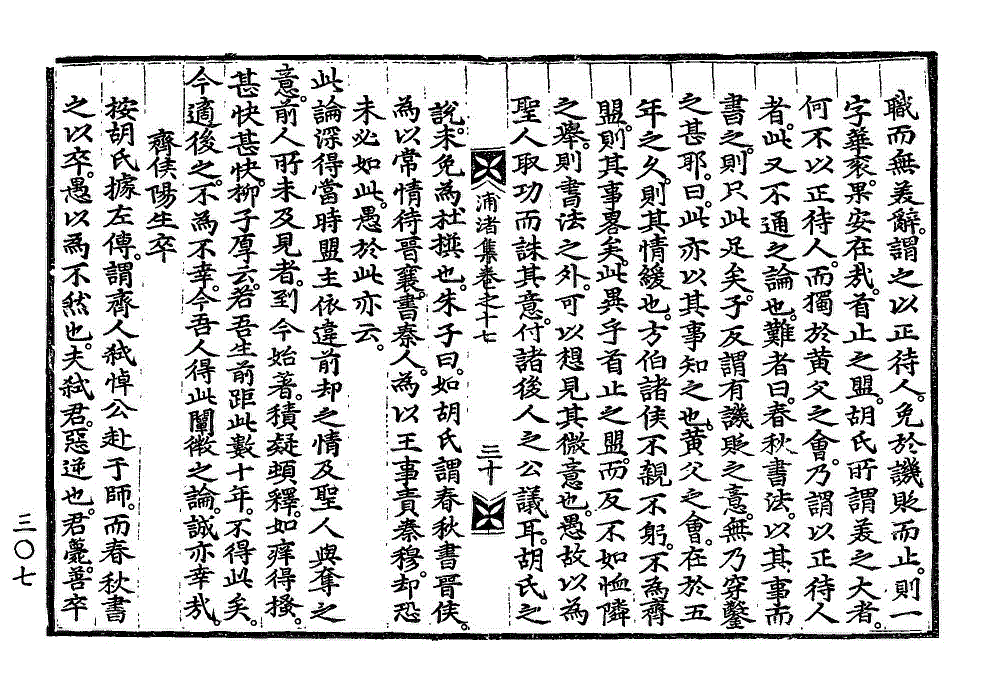 职而无美辞。谓之以正待人。免于讥贬而止。则一字华衮。果安在哉。首止之盟。胡氏所谓美之大者。何不以正待人。而独于黄父之会。乃谓以正待人者。此又不通之论也。难者曰。春秋书法。以其事而书之。则只此足矣。子反谓有讥贬之意。无乃穿凿之甚耶。曰。此亦以其事知之也。黄父之会。在于五年之久。则其情缓也。方伯诸侯不亲不躬。不为齐盟。则其事略矣。此异乎首止之盟。而反不如恤邻之举。则书法之外。可以想见其微意也。愚故以为圣人取功而诛其意。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胡氏之说。未免为杜撰也。朱子曰。如胡氏谓春秋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却恐未必如此。愚于此亦云。
职而无美辞。谓之以正待人。免于讥贬而止。则一字华衮。果安在哉。首止之盟。胡氏所谓美之大者。何不以正待人。而独于黄父之会。乃谓以正待人者。此又不通之论也。难者曰。春秋书法。以其事而书之。则只此足矣。子反谓有讥贬之意。无乃穿凿之甚耶。曰。此亦以其事知之也。黄父之会。在于五年之久。则其情缓也。方伯诸侯不亲不躬。不为齐盟。则其事略矣。此异乎首止之盟。而反不如恤邻之举。则书法之外。可以想见其微意也。愚故以为圣人取功而诛其意。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胡氏之说。未免为杜撰也。朱子曰。如胡氏谓春秋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却恐未必如此。愚于此亦云。此论深得当时盟主依违前却之情及圣人与夺之意。前人所未及见者。到今始著。积疑顿释。如痒得搔。甚快甚快。柳子厚云。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不得此矣。今适后之。不为不幸。今吾人得此阐微之论。诚亦幸哉。
齐侯阳生卒
按胡氏据左传。谓齐人弑悼公赴于师。而春秋书之以卒。愚以为不然也。夫弑君。恶逆也。君薨。善卒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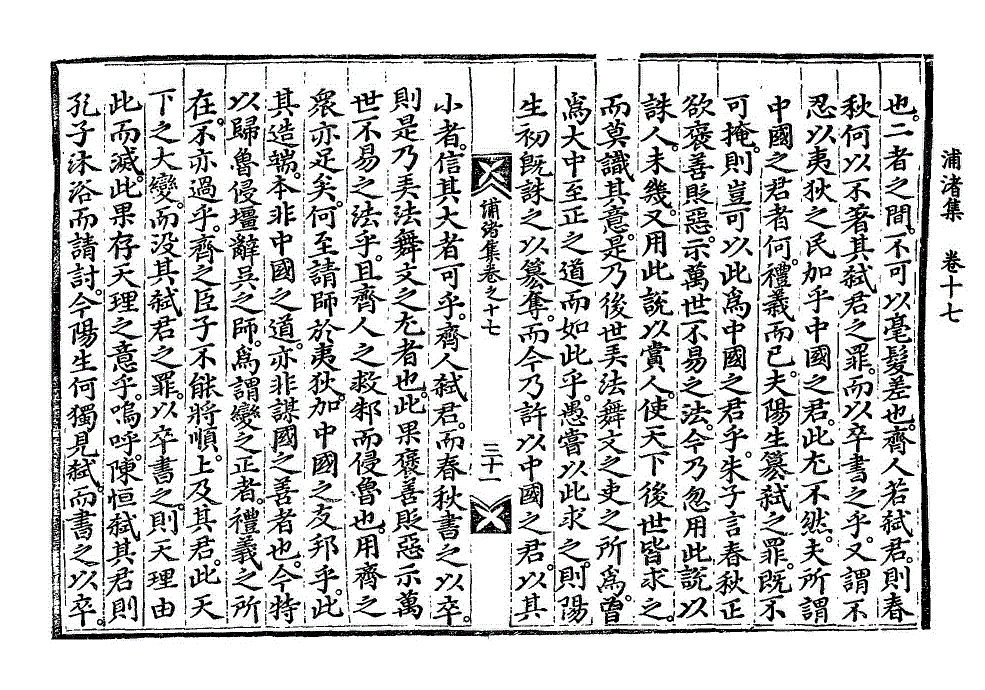 也。二者之间。不可以毫发差也。齐人若弑君。则春秋何以不著其弑君之罪。而以卒书之乎。又谓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此尤不然。夫所谓中国之君者何。禯义而已。夫阳生篡弑之罪。既不可掩。则岂可以此为中国之君乎。朱子言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也’字를 보충해 넣었다.)。曾为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愚尝以此求之。则阳生初既诛之以篡夺。而今乃许以中国之君。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可乎。齐人弑君。而春秋书之以卒。则是乃弄法舞文之尤者也。此果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乎。且齐人之救邾而侵鲁也。用齐之众亦足矣。何至请师于夷狄。加中国之友邦乎。此其造端。本非中国之道。亦非谋国之善有也。今特以归鲁侵疆辞吴之师。为谓变之正者。礼义之所在。不亦过乎。齐之臣子不能将顺。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变。而没其弑君之罪。以卒书之。则天理由此而灭。此果存天理之意乎。呜呼。陈恒弑其君则孔子沐浴而请讨。今阳生何独见弑。而书之以卒。
也。二者之间。不可以毫发差也。齐人若弑君。则春秋何以不著其弑君之罪。而以卒书之乎。又谓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此尤不然。夫所谓中国之君者何。禯义而已。夫阳生篡弑之罪。既不可掩。则岂可以此为中国之君乎。朱子言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也’字를 보충해 넣었다.)。曾为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愚尝以此求之。则阳生初既诛之以篡夺。而今乃许以中国之君。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可乎。齐人弑君。而春秋书之以卒。则是乃弄法舞文之尤者也。此果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乎。且齐人之救邾而侵鲁也。用齐之众亦足矣。何至请师于夷狄。加中国之友邦乎。此其造端。本非中国之道。亦非谋国之善有也。今特以归鲁侵疆辞吴之师。为谓变之正者。礼义之所在。不亦过乎。齐之臣子不能将顺。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变。而没其弑君之罪。以卒书之。则天理由此而灭。此果存天理之意乎。呜呼。陈恒弑其君则孔子沐浴而请讨。今阳生何独见弑。而书之以卒。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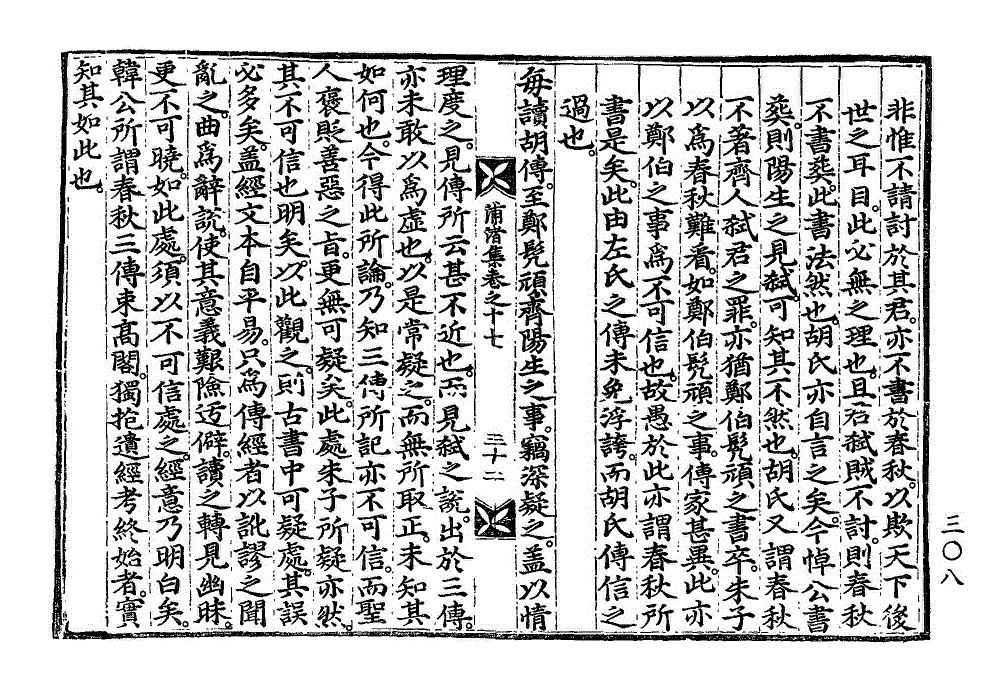 非惟不请讨于其君。亦不书于春秋。以欺天下后世之耳目。此必无之理也。且君弑贼不讨。则春秋不书葬。此书法然也。胡氏亦自言之矣。今悼公书葬。则阳生之见弑。可知其不然也。胡氏又谓春秋不著齐人弑君之罪。亦犹郑伯髡顽之书卒。朱子以为春秋难看。如郑伯髡顽之事。传家甚异。此亦以郑伯之事为不可信也。故愚于此亦谓春秋所书是矣。此由左氏之传未免浮誇。而胡氏传信之过也。
非惟不请讨于其君。亦不书于春秋。以欺天下后世之耳目。此必无之理也。且君弑贼不讨。则春秋不书葬。此书法然也。胡氏亦自言之矣。今悼公书葬。则阳生之见弑。可知其不然也。胡氏又谓春秋不著齐人弑君之罪。亦犹郑伯髡顽之书卒。朱子以为春秋难看。如郑伯髡顽之事。传家甚异。此亦以郑伯之事为不可信也。故愚于此亦谓春秋所书是矣。此由左氏之传未免浮誇。而胡氏传信之过也。每读胡传。至郑髡顽,齐阳生之事。窃深疑之。盖以情理度之。见传所云甚不近也。而见弑之说。出于三传。亦未敢以为虚也。以是常疑之。而无所取正。未知其如何也。今得此所论。乃知三传所记亦不可信。而圣人褒贬善恶之旨。更无可疑矣。此处朱子所疑亦然。其不可信也明矣。以此观之。则古书中可疑处。其误必多矣。盖经文本自平易。只为传经者以讹谬之闻乱之。曲为辞说。使其意义艰险迂僻。读之转见幽昧。更不可晓。如此处。须以不可信处之。经意乃明白矣。韩公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考终始者。实知其如此也。
答安牛山(邦俊)书
郡人之来。伏承兄惠翰。就审闲中起居佳胜。仰慰仰慰。仆得病一年有馀。近者沈困益甚。闷闷。示所著义录。谨已一览。得见南方十数义士诚节烈烈。真可起敬于百代。而非兄勤勤裒聚。著于此录。其义烈可传之迹。不至于湮灭乎。君子贵乐道人之善。兄之志真不愧古君子。而此十数人义魄。亦且感慨于冥冥矣。仆敢不缀于其后。以少助兄之志。而近缘呻痛方苦。来人又忙返未及焉。当俟贱疾稍间。谨构思以附后便也。
答安牛山书(附元书)
秋凉。伏惟令起居万福。区区瞻慰。生衰病日深。就木不远。未死前一奉。唯日望之。而京乡隔绝。梦寐不到。奈如之何。然其向慕之诚。不敢自疏外于大君子。年前与楸相往复书。谨以别纸录呈。幸留心省察。且尽日垂竿俯碧流。鱼贪芳饵竞吞钩。前鱼登钓后鱼进。闲倚苔矶笑未休。此诗生曾闻于人。不知谁氏所作。或云柳进士。而其名亦不传。兄如有闻知。示及。今去梁砥南及朱上舍晔。同志之友也。闻兄与生相切。欲夤缘拜谒。命坐赐言。以代故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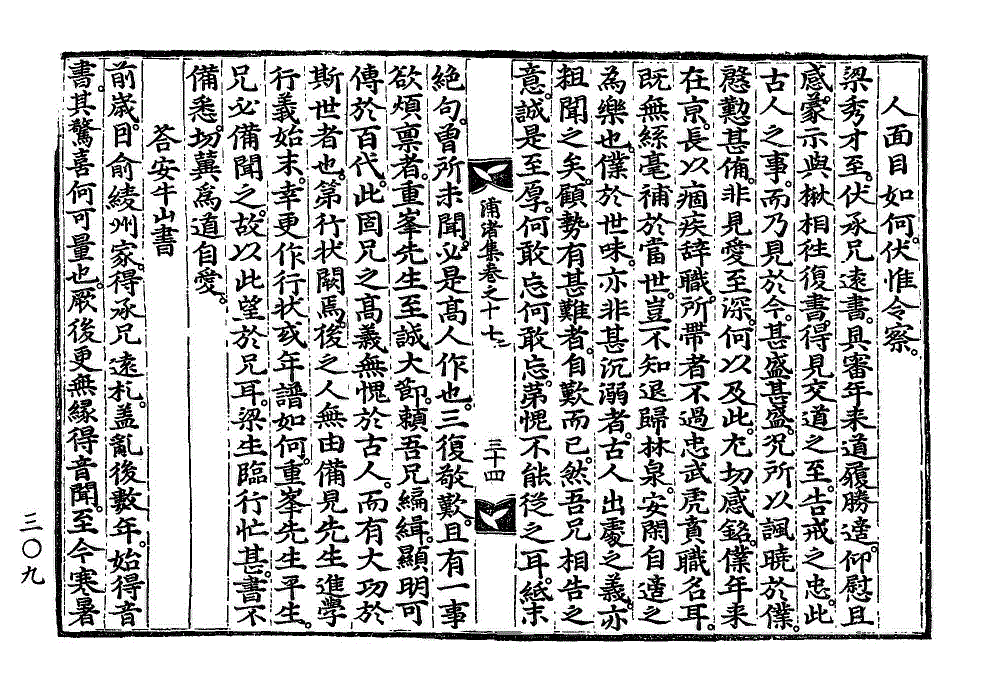 人面目如何。伏惟令察。
人面目如何。伏惟令察。梁秀才至。伏承兄远书。具审年来道履胜适。仰慰且感。蒙示与楸相往复书。得见交道之至。告戒之忠。此古人之事。而乃见于今。甚盛甚盛。况所以讽晓于仆。慇勤甚备。非见爱至深。何以及此。尤切感铭。仆年来在京。长以痼疾辞职。所带者不过忠武虎贲职名耳。既无丝毫补于当世。岂不知退归林泉。安闲自适之为乐也。仆于世味。亦非甚沈溺者。古人出处之义。亦粗闻之矣。顾势有甚难者。自叹而已。然吾兄相告之意。诚是至厚。何敢忘何敢忘。第愧不能从之耳。纸末绝句。曾所未闻。必是高人作也。三复敬叹。且有一事欲烦禀者。重峰先生至诚大节。赖吾兄编缉。显明可传于百代。此固兄之高义无愧于古人。而有大功于斯世者也。第行状阙焉。后之人无由备见先生进学行义始末。幸更作行状或年谱如何。重峰先生平生。兄必备闻之。故以此望于兄耳。梁生临行忙甚。书不备悉。切冀为道自爱。
答安牛山书
前岁。因俞绫州家。得承兄远札。盖乱后数年。始得音书。其惊喜何可量也。厥后更无缘得音闻。至今寒暑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0H 页
 已再易矣。瞻恋一念。何尝不驰于湖海之南也。所示盛文三篇。据證赡博。辞旨畅达。明白严正。诚可起敬百代。不胜叹服叹服。每敛衽庄读。如亲对清仪而承警咳也。跋语。谨构草已久。盖粗以效其区区敬叹之意。而于盛篇。岂能有所发明也。顾相望千里。无由送致。今因光州之行。并本稿寓呈。计不至浮沈也。第其间辞语或有似太阳深證。使世人见则切齿者必多。切幸兄默观焉。勿使挂人眼如何。时事至此。虽在畎亩。岂堪愤闷。想兄素刚介。其伤世之念。又何可胜焉。且想山林日长。所论著必多。于此三篇。亦可见矣。恨无由得一遍观之以自励也。仆亦于闲中。无以遣日。著得数卷书。亦恨远不得就正也。所怀千万。无由一吐。第南望怅然而已。切冀千万自爱。以慰瞻系。不宣。
已再易矣。瞻恋一念。何尝不驰于湖海之南也。所示盛文三篇。据證赡博。辞旨畅达。明白严正。诚可起敬百代。不胜叹服叹服。每敛衽庄读。如亲对清仪而承警咳也。跋语。谨构草已久。盖粗以效其区区敬叹之意。而于盛篇。岂能有所发明也。顾相望千里。无由送致。今因光州之行。并本稿寓呈。计不至浮沈也。第其间辞语或有似太阳深證。使世人见则切齿者必多。切幸兄默观焉。勿使挂人眼如何。时事至此。虽在畎亩。岂堪愤闷。想兄素刚介。其伤世之念。又何可胜焉。且想山林日长。所论著必多。于此三篇。亦可见矣。恨无由得一遍观之以自励也。仆亦于闲中。无以遣日。著得数卷书。亦恨远不得就正也。所怀千万。无由一吐。第南望怅然而已。切冀千万自爱。以慰瞻系。不宣。答安牛山书
虑外。忽承老兄千里书问。展读惊喜。反复不置。因审物外起处万佳。尤切感慰。且蒙寄示重峰先生当时与诸人论议事大略。得见先生持己接人之正。皆曾所未闻。极令人感叹而兴起。昨者与裴宗度语。因及先生事。仆谓先生一生事迹可法者。若不记录。恐至泯没。实为千载之恨。今世惟老兄知先生事。其明日。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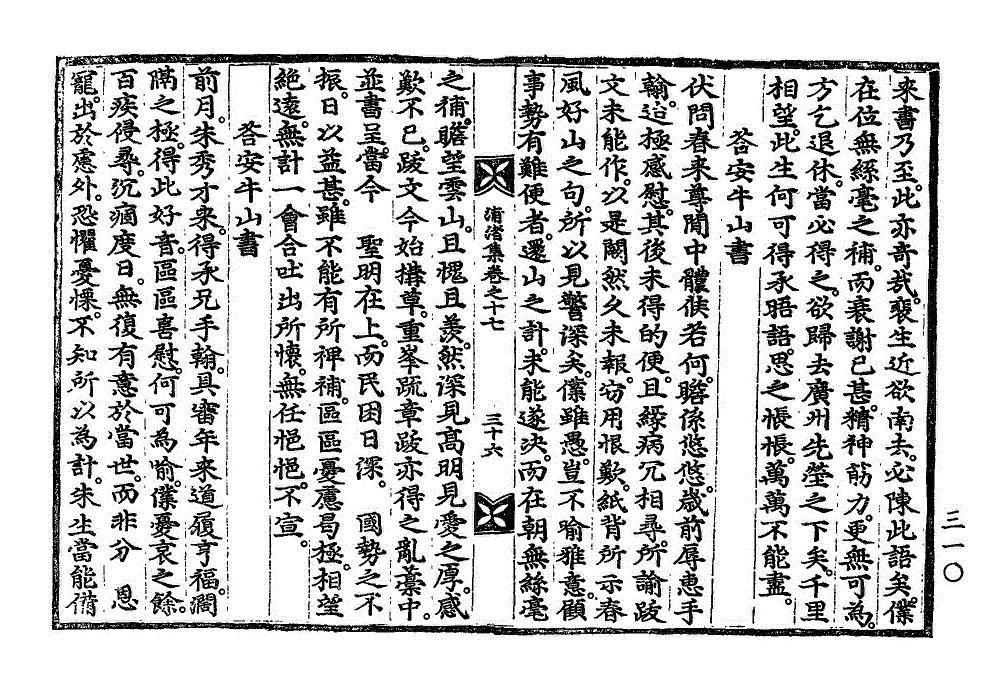 来书乃至。此亦奇哉。裴生近欲南去。必陈此语矣。仆在位无丝毫之补。而衰谢已甚。精神筋力。更无可为。方乞退休。当必得之。欲归去广州先茔之下矣。千里相望。此生何可得承晤语。思之怅怅。万万不能尽。
来书乃至。此亦奇哉。裴生近欲南去。必陈此语矣。仆在位无丝毫之补。而衰谢已甚。精神筋力。更无可为。方乞退休。当必得之。欲归去广州先茔之下矣。千里相望。此生何可得承晤语。思之怅怅。万万不能尽。答安牛山书
伏问春来尊间中体候若何。瞻系悠悠。岁前辱惠手翰。迨极感慰。其后未得的便。且缘病冗相寻。所谕跋文未能作。以是阙然久未报。窃用恨叹。纸背所示春风好山之句。所以见警深矣。仆虽愚。岂不喻雅意。顾事势有难便者。还山之计。未能遂决。而在朝无丝毫之补。瞻望云山。且愧且羡。然深见高明见爱之厚。感叹不已。跋文今始构草。重峰疏章跋亦得之乱稿中。并书呈。当今 圣明在上。而民困日深。 国势之不振。日以益甚。虽不能有所裨补。区区忧虑曷极。相望绝远。无计一会合吐出所怀。无任悒悒。不宣。
答安牛山书
前月。朱秀才来。得承兄手翰。具审年来道履亨福。阔隔之极。得此好音。区区喜慰。何可为喻。仆忧哀之馀。百疾侵寻。沈痼度日。无复有意于当世。而非分 恩宠。出于虑外。恐惧忧慄。不知所以为计。朱生当能备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1H 页
 道此间怀绪矣。示来延平书及晋州记事。深见老兄贤贤慕义之意久而愈笃。钦感不已。忝窃朝端。无分毫裨补于世。而事势又牵缀。欲退不得。俯仰愧怍。未得善计。徒积忧悯而已。南望杳杳。无由一见君子以道此怀。第切叹慨。不宣。
道此间怀绪矣。示来延平书及晋州记事。深见老兄贤贤慕义之意久而愈笃。钦感不已。忝窃朝端。无分毫裨补于世。而事势又牵缀。欲退不得。俯仰愧怍。未得善计。徒积忧悯而已。南望杳杳。无由一见君子以道此怀。第切叹慨。不宣。答安牛山书
瞻恋中伏承老兄千里书问。区区慰喜何可言。第审感疾日久。尚未平复。窃不胜仰虑。唯冀十分善调。速就平和之境。前日所论名贤真儒之异。则诚是确论。盖所谓真儒者。必须直以孔颜为法。不以一毫未尽之道自期待焉者。方是真儒也。然则所谓真儒。岂非古今所绝少者也。自古贤者未必皆如是。圣人许子文武(一作文)子以忠清。而不许其为仁。以此也。老兄此论。诚见吾儒高致。非人人所可到也。敢不敬服也哉。所惠乾橘。仰感。不宣。
答安牛山书(附元书)
谨问冬寒。静候何如。悬念无已。弟依旧。此去草鞋。乃三神山旧伴使我传致于兄也。出处进退。俱系此鞋。兄其领纳。
春间。尝得承令兄千里手翰。具审年岁来兄静里体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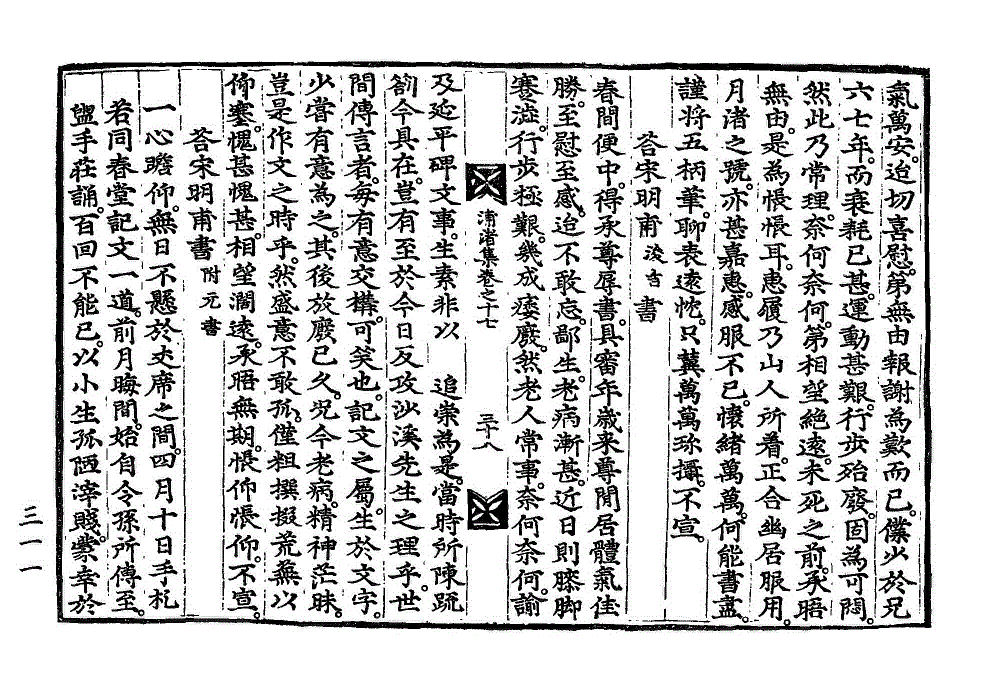 气万安。迨切喜慰。第无由报谢为叹而已。仆少于兄六七年。而衰耗已甚。运动甚艰。行步殆废。固为可闷。然此乃常理。奈何奈何。第相望绝远。未死之前。承晤无由。是为怅怅耳。患履乃山人所着。正合幽居服用。月渚之号。亦甚嘉惠。感服不已。怀绪万万。何能书尽。谨将五柄笔。聊表远忱。只冀万万珍摄。不宣。
气万安。迨切喜慰。第无由报谢为叹而已。仆少于兄六七年。而衰耗已甚。运动甚艰。行步殆废。固为可闷。然此乃常理。奈何奈何。第相望绝远。未死之前。承晤无由。是为怅怅耳。患履乃山人所着。正合幽居服用。月渚之号。亦甚嘉惠。感服不已。怀绪万万。何能书尽。谨将五柄笔。聊表远忱。只冀万万珍摄。不宣。答宋明甫(浚吉)书
春间便中。得承尊辱书。具审年岁来尊閒居体气佳胜。至慰至感。迨不敢忘。鄙生。老病渐甚。近日则膝脚蹇涩。行步极艰。几成痿废。然老人常事。奈何奈何。谕及延平碑文事。生素非以 追崇为是。当时所陈疏劄今具在。岂有至于今日反攻沙溪先生之理乎。世间传言者。每有意交构。可笑也。记文之属。生于文字。少尝有意为之。其后放废已久。况今老病。精神茫昧。岂是作文之时乎。然盛意不敢孤。仅粗撰掇荒芜以仰塞。愧甚愧甚。相望阔远。承晤无期。怅仰怅仰。不宣。
答宋明甫书(附元书)
一心瞻仰。无日不悬于丈席之间。四月十日手札若同春堂记文一道。前月晦间。始自令孙所传至。盥手庄诵。百回不能已。以小生孤陋滓贱。蒙幸于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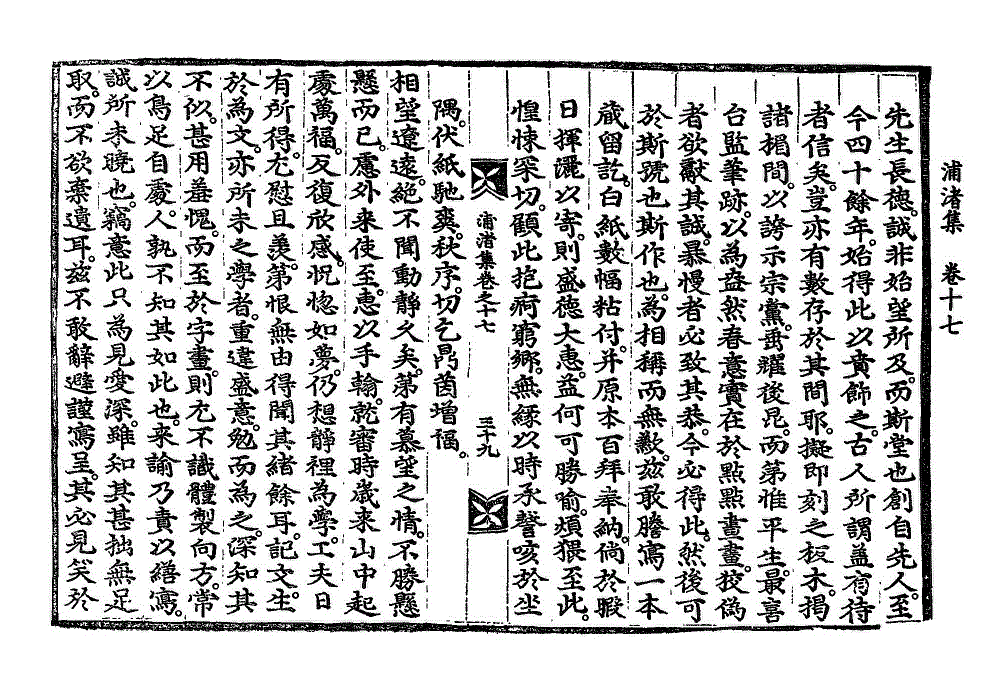 先生长德。诚非始望所及。而斯堂也创自先人。至今四十馀年。始得此以贵饰之。古人所谓盖有待者信矣。岂亦有数存于其间耶。拟即刻之板木。揭诸楣间。以誇示宗党。垂耀后昆。而第惟平生。最喜台监笔迹。以为盎然春意实在于点点画画。狡伪者欲献其诚。暴慢者必致其恭。今必得此。然后可于斯号也斯作也。为相称而无歉。兹敢誊写一本藏留讫。白纸数幅粘付。并原本百拜奉纳。倘于暇日挥洒以寄。则盛德大惠。益何可胜喻。烦猥至此。惶悚深切。顾此抱痾穷乡。无缘以时承謦咳于坐隅。伏纸驰爽。秋序。切乞鼎茵增福。
先生长德。诚非始望所及。而斯堂也创自先人。至今四十馀年。始得此以贵饰之。古人所谓盖有待者信矣。岂亦有数存于其间耶。拟即刻之板木。揭诸楣间。以誇示宗党。垂耀后昆。而第惟平生。最喜台监笔迹。以为盎然春意实在于点点画画。狡伪者欲献其诚。暴慢者必致其恭。今必得此。然后可于斯号也斯作也。为相称而无歉。兹敢誊写一本藏留讫。白纸数幅粘付。并原本百拜奉纳。倘于暇日挥洒以寄。则盛德大惠。益何可胜喻。烦猥至此。惶悚深切。顾此抱痾穷乡。无缘以时承謦咳于坐隅。伏纸驰爽。秋序。切乞鼎茵增福。相望辽远。绝不闻动静久矣。第有慕望之情。不胜悬悬而已。虑外来使至。惠以手翰。就审时岁来山中起处万福。反复欣感。恍惚如梦。仍想静里为学。工夫日有所得。尤慰且羡。第恨无由得闻其绪馀耳。记文。生于为文。亦所未之学者。重违盛意。勉而为之。深知其不似。甚用羞愧。而至于字画。则尤不识体制向方。常以鸟足自处。人孰不知其如此也。来谕乃责以缮写。诚所未晓也。窃意此只为见爱深。虽知其甚拙无足取。而不欲弃遗耳。兹不敢辞避谨写呈。其必见笑于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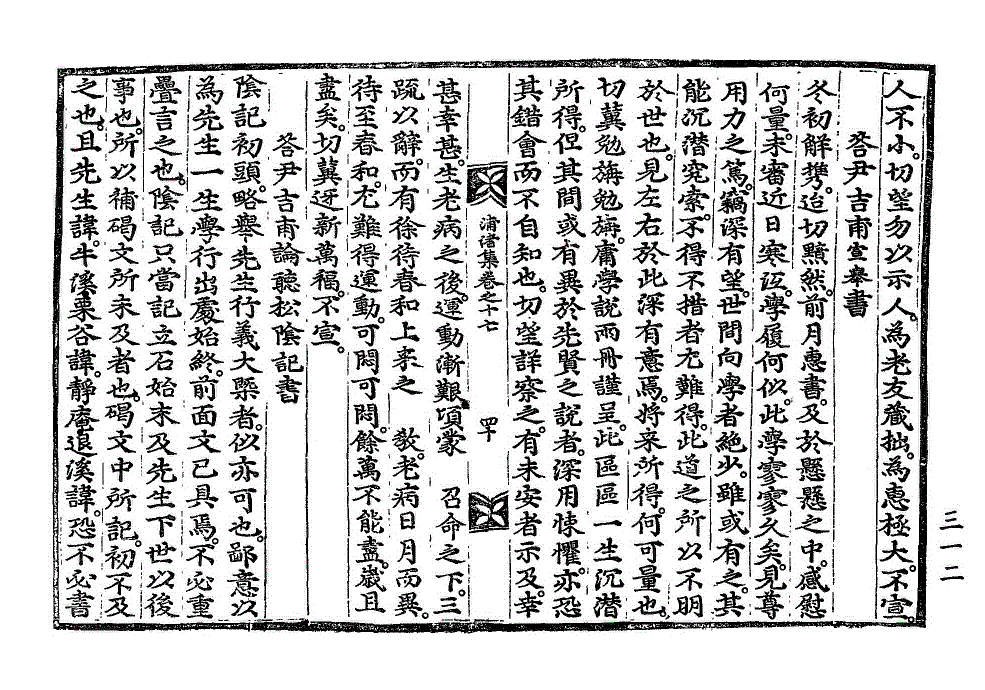 人不小。切望勿以示人。为老友藏拙。为惠极大。不宣。
人不小。切望勿以示人。为老友藏拙。为惠极大。不宣。答尹吉甫(宣举)书
冬初解携。迨切黯然。前月惠书。及于悬悬之中。感慰何量。未审近日寒冱。学履何似。此学寥寥久矣。见尊用力之笃。窃深有望。世间向学者绝少。虽或有之。其能沈潜究索。不得不措者尤难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于世也。见左右于此深有意焉。将来所得。何可量也。切冀勉旃勉旃。庸学说两册谨呈。此区区一生沈潜所得。但其间或有异于先贤之说者。深用悚惧。亦恐其错会而不自知也。切望详察之。有未安者示及。幸甚幸甚。生老病之后。运动渐艰。顷蒙 召命之下。三疏以辞。而有徐待春和上来之 教。老病日月而异。待至春和。尤难得运动。可闷可闷。馀万不能尽。岁且尽矣。切冀迓新万福。不宣。
答尹吉甫论听松阴记书
阴记初头。略举先生行义大概者。似亦可也。鄙意以为先生一生学行出处始终。前面文已具焉。不必重叠言之也。阴记只当记立石始末及先生下世以后事也。所以补碣文所未及者也。碣文中所记。初不及之也。且先生讳。牛溪,栗谷讳。静庵,退溪讳。恐不必书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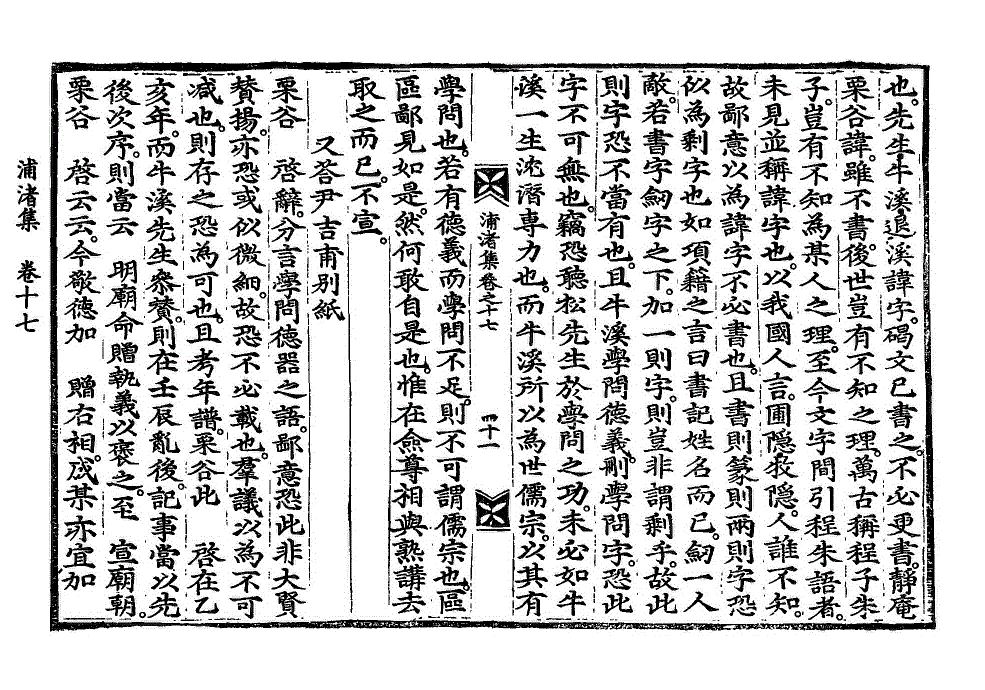 也。先生,牛溪,退溪讳字。碣文已书之。不必更书。静庵栗谷讳。虽不书。后世岂有不知之理。万古称程子朱子。岂有不知为某人之理。至今文字间引程朱语者。未见并称讳字也。以我国人言。圃隐,牧隐。人谁不知。故鄙意以为讳字不必书也。且书则篆则两则字恐似为剩字也如项籍之言曰书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若书字剑字之下。加一则字。则岂非谓剩乎。故此则字恐不当有也。且牛溪学问德义。删学问字。恐此字不可无也。窃恐听松先生于学问之功。未必如牛溪一生沈潜专力也。而牛溪所以为世儒宗。以其有学问也。若有德义而学问不足。则不可谓儒宗也。区区鄙见如是。然何敢自是也。惟在佥尊相与熟讲去取之而已。不宣。
也。先生,牛溪,退溪讳字。碣文已书之。不必更书。静庵栗谷讳。虽不书。后世岂有不知之理。万古称程子朱子。岂有不知为某人之理。至今文字间引程朱语者。未见并称讳字也。以我国人言。圃隐,牧隐。人谁不知。故鄙意以为讳字不必书也。且书则篆则两则字恐似为剩字也如项籍之言曰书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若书字剑字之下。加一则字。则岂非谓剩乎。故此则字恐不当有也。且牛溪学问德义。删学问字。恐此字不可无也。窃恐听松先生于学问之功。未必如牛溪一生沈潜专力也。而牛溪所以为世儒宗。以其有学问也。若有德义而学问不足。则不可谓儒宗也。区区鄙见如是。然何敢自是也。惟在佥尊相与熟讲去取之而已。不宣。又答尹吉甫别纸
栗谷 启辞。分言学问德器之语。鄙意恐此非大贤赞扬。亦恐或似微细。故恐不必载也。群议以为不可减也。则存之恐为可也。且考年谱。栗谷此 启在乙亥年。而牛溪先生参赞。则在壬辰乱后。记事当以先后次序。则当云 明庙命赠执义以褒之。至 宣庙朝。栗谷 启云云。今敬德加 赠右相。成某亦宜加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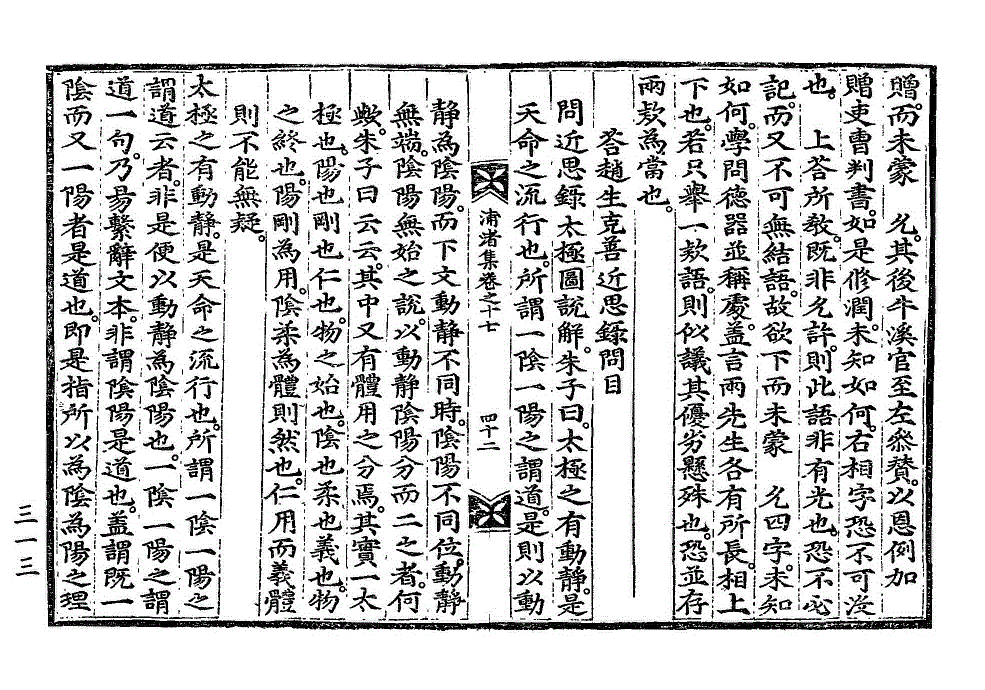 赠。而未蒙 允。其后牛溪官至左参赞。以恩例加 赠吏曹判书。如是修润。未知如何。右相字恐不可没也。 上答所教。既非允许。则此语非有光也。恐不必记。而又不可无结语。故欲下而未蒙 允四字。未知如何。学问德器并称处。盖言两先生各有所长。相上下也。若只举一款语。则似议其优劣悬殊也。恐并存两款为当也。
赠。而未蒙 允。其后牛溪官至左参赞。以恩例加 赠吏曹判书。如是修润。未知如何。右相字恐不可没也。 上答所教。既非允许。则此语非有光也。恐不必记。而又不可无结语。故欲下而未蒙 允四字。未知如何。学问德器并称处。盖言两先生各有所长。相上下也。若只举一款语。则似议其优劣悬殊也。恐并存两款为当也。答赵生克善近思录问目
问近思录太极图说解。朱子曰。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则以动静为阴阳。而下文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说。以动静阴阳分而二之者。何欤。朱子曰云云。其中又有体用之分焉。其实一太极也。阳也刚也仁也。物之始也。阴也柔也义也。物之终也。阳刚为用。阴柔为体则然也。仁用而义体则不能无疑。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云者。非是便以动静为阴阳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句。乃易系辞文本。非谓阴阳是道也。盖谓既一阴而又一阳者是道也。即是指所以为阴为阳之理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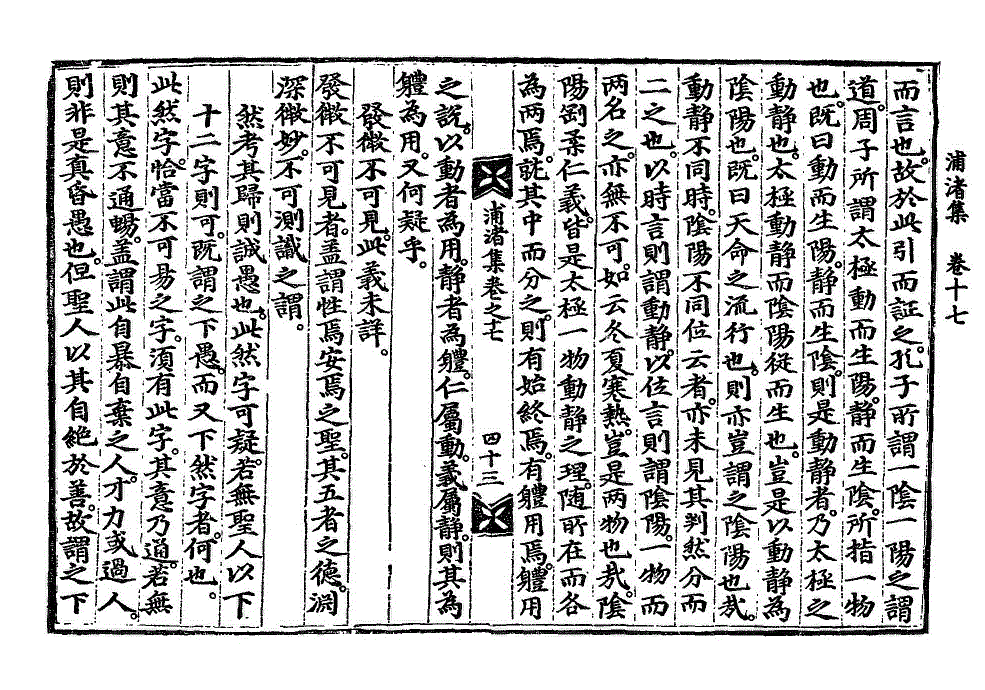 而言也。故于此引而證之。孔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所指一物也。既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是动静者。乃太极之动静也。太极动静而阴阳从而生也。岂是以动静为阴阳也。既曰天命之流行也。则亦岂谓之阴阳也哉。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云者。亦未见其判然分而二之也。以时言则谓动静。以位言则谓阴阳。一物而两名之。亦无不可。如云冬夏寒热。岂是两物也哉。阴阳刚柔仁义。皆是太极一物动静之理。随所在而各为两焉。就其中而分之。则有始终焉。有体用焉。体用之说。以动者为用。静者为体。仁属动。义属静。则其为体为用。又何疑乎。
而言也。故于此引而證之。孔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所指一物也。既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是动静者。乃太极之动静也。太极动静而阴阳从而生也。岂是以动静为阴阳也。既曰天命之流行也。则亦岂谓之阴阳也哉。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云者。亦未见其判然分而二之也。以时言则谓动静。以位言则谓阴阳。一物而两名之。亦无不可。如云冬夏寒热。岂是两物也哉。阴阳刚柔仁义。皆是太极一物动静之理。随所在而各为两焉。就其中而分之。则有始终焉。有体用焉。体用之说。以动者为用。静者为体。仁属动。义属静。则其为体为用。又何疑乎。发微不可见。此义未详。
发微不可见者。盖谓性焉安焉之圣。其五者之德。渊深微妙。不可测识之谓。
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此然字可疑。若无圣人以下十二字则可。既谓之下愚。而又下然字者。何也。
此然字。恰当不可易之字。须有此字。其意乃通。若无则其意不通畅。盖谓此自暴自弃之人。才力或过人。则非是真昏愚也。但圣人以其自绝于善。故谓之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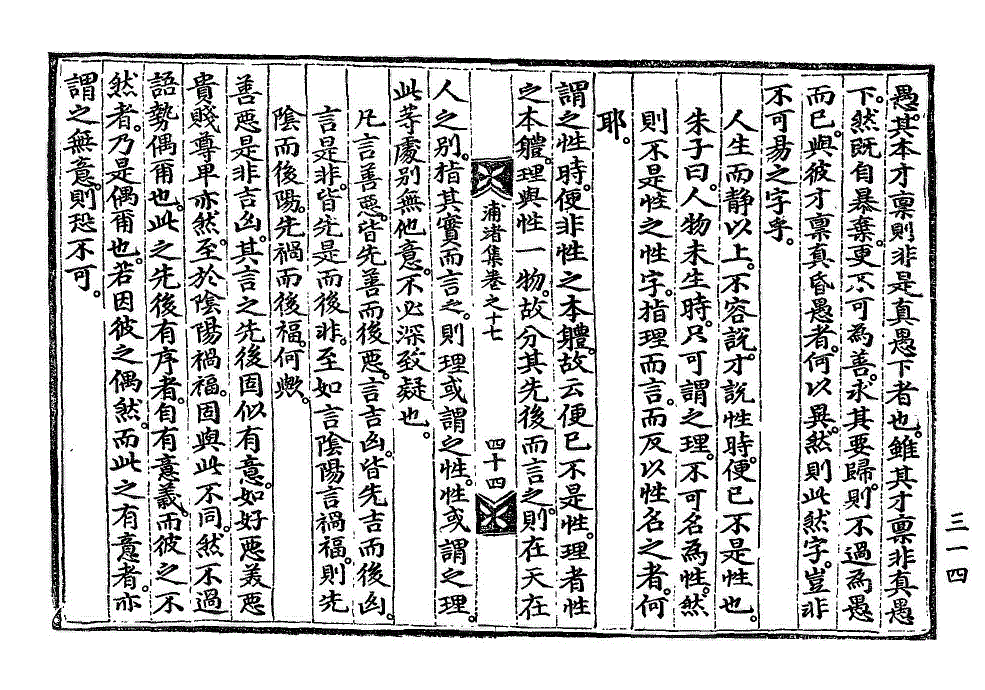 愚。其本才禀则非是真愚下者也。虽其才禀非真愚下。然既自暴弃。更不可为善。求其要归。则不过为愚而已。与彼才禀真昏愚者。何以异。然则此然字。岂非不可易之字乎。
愚。其本才禀则非是真愚下者也。虽其才禀非真愚下。然既自暴弃。更不可为善。求其要归。则不过为愚而已。与彼才禀真昏愚者。何以异。然则此然字。岂非不可易之字乎。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不可名为性。然则不是性之性字。指理而言。而反以性名之者。何耶。
谓之性时。使非性之本体。故云便已不是性。理者性之本体。理与性一物。故分其先后而言之。则在天在人之别。指其实而言之。则理或谓之性。性或谓之理。此等处别无他意。不必深致疑也。
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至如言阴阳言祸福。则先阴而后阳。先祸而后福。何欤。
善恶是非吉凶。其言之先后固似有意。如好恶美恶贵贱尊卑亦然。至于阴阳祸福。固与此不同。然不过语势偶尔也。此之先后有序者。自有意义。而彼之不然者。乃是偶尔也。若因彼之偶然。而此之有意者。亦谓之无意。则恐不可。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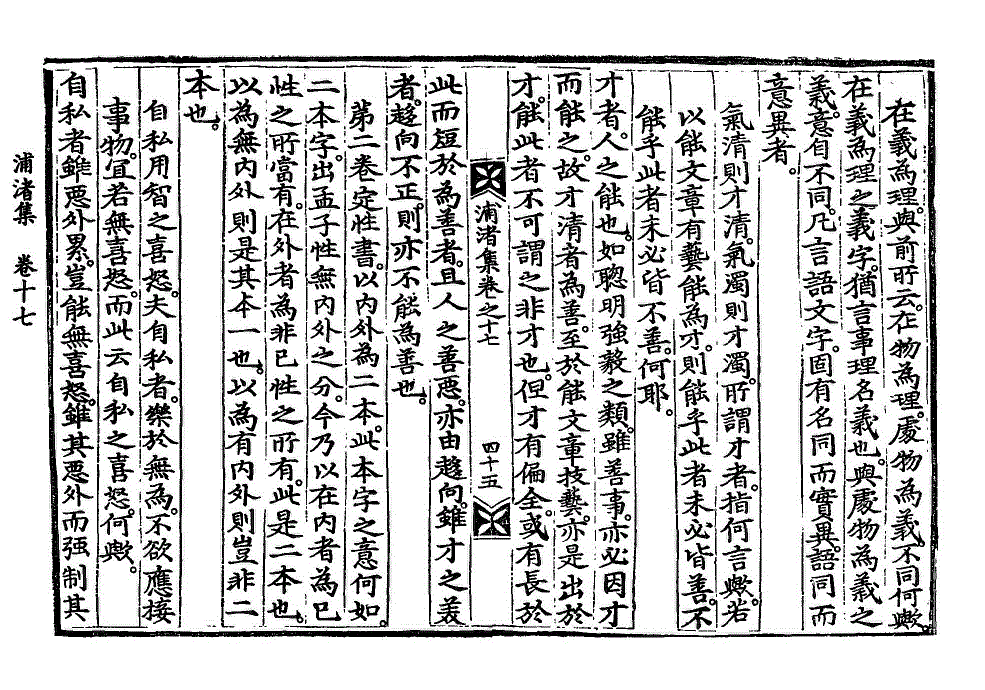 在义为理。与前所云。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不同何欤。
在义为理。与前所云。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不同何欤。在义为理之义字。犹言事理名义也。与处物为义之义。意自不同。凡言语文字。固有名同而实异。语同而意异者。
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所谓才者。指何言欤。若以能文章有艺能为才。则能乎此者未必皆善。不能乎此者未必皆不善。何耶。
才者。人之能也。如聪明强毅之类。虽善事。亦必因才而能之。故才清者为善。至于能文章技艺。亦是出于才。能此者不可谓之非才也。但才有偏全。或有长于此而短于为善者。且人之善恶。亦由趋向。虽才之美者。趋向不正。则亦不能为善也。
第二卷定性书。以内外为二本。此本字之意何如。
二本字。出孟子性无内外之分。今乃以在内者为己性之所当有。在外者为非己性之所有。此是二本也。以为无内外则是其本一也。以为有内外则岂非二本也。
自私用智之喜怒。夫自私者。乐于无为。不欲应接事物。宜若无喜怒。而此云自私之喜怒。何欤。
自私者虽恶外累。岂能无喜怒。虽其恶外而强制其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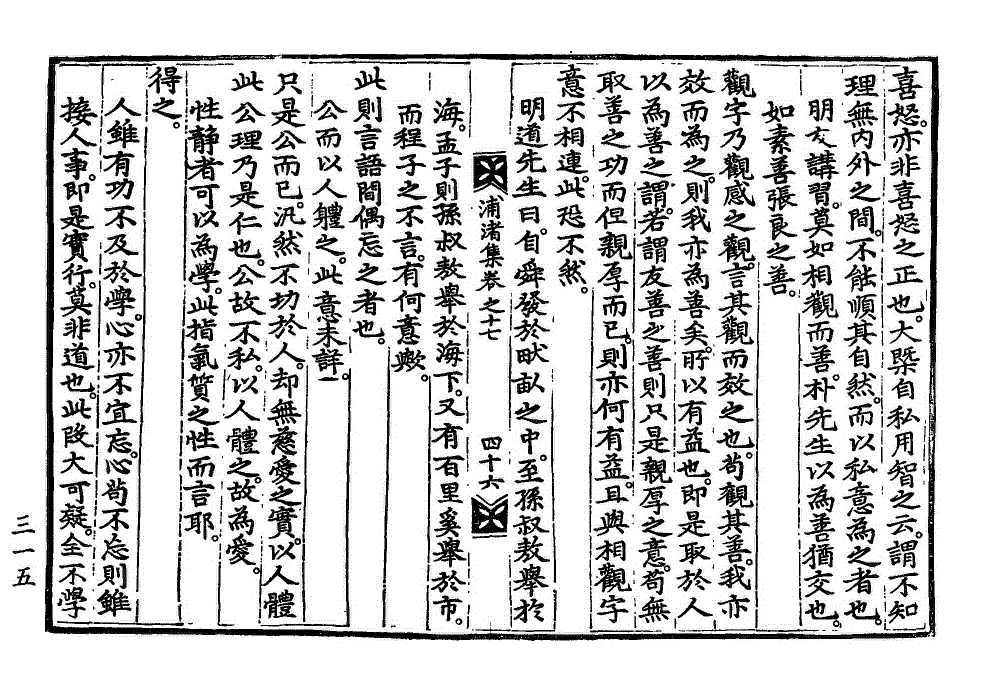 喜怒。亦非喜怒之正也。大概自私用智之云。谓不知理无内外之间。不能顺其自然。而以私意为之者也。
喜怒。亦非喜怒之正也。大概自私用智之云。谓不知理无内外之间。不能顺其自然。而以私意为之者也。朋友讲习。莫如相观而善。朴先生以为善犹交也。如素善张良之善。
观字乃观感之观。言其观而效之也。苟观其善。我亦效而为之。则我亦为善矣。所以有益也。即是取于人以为善之谓。若谓友善之善则只是亲厚之意。苟无取善之功而但亲厚而已。则亦何有益。且与相观字意不相连。此恐不然。
明道先生曰。自舜发于畎亩之中。至孙叔敖举于海。孟子则孙叔敖举于海下。又有百里奚举于市。而程子之不言。有何意欤。
此则言语间偶忘之者也。
公而以人体之。此意未详。
只是公而已。汎然不切于人。却无慈爱之实。以人体此公理乃是仁也。公故不私。以人体之。故为爱。
性静者可以为学。此指气质之性而言耶。
得之。
人虽有功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此段大可疑。全不学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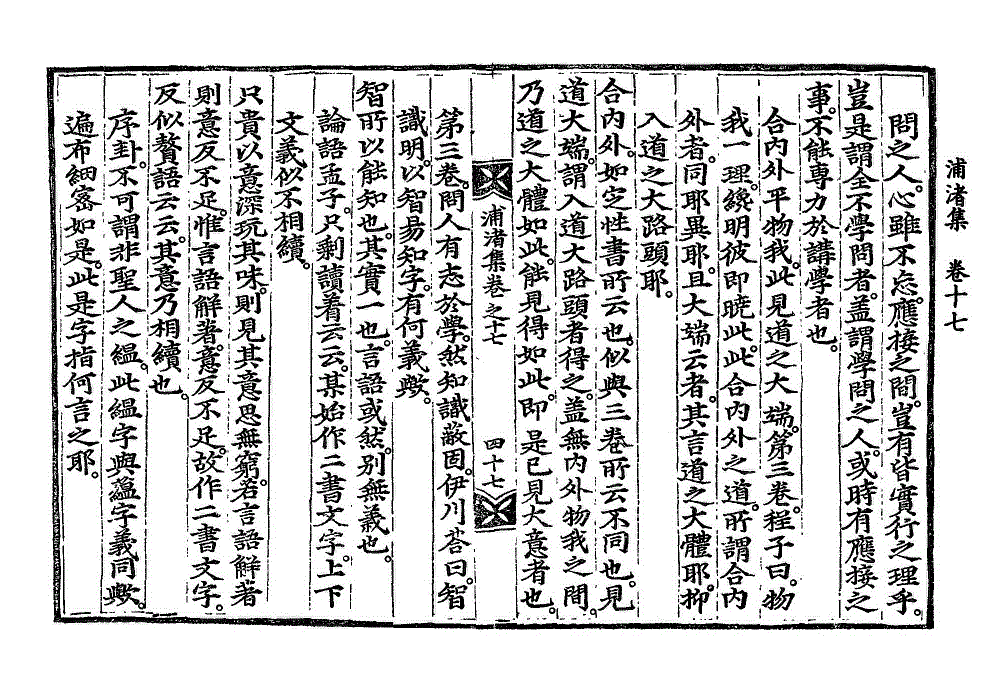 问之人。心虽不忘。应接之间。岂有皆实行之理乎。
问之人。心虽不忘。应接之间。岂有皆实行之理乎。岂是谓全不学问者。盖谓学问之人。或时有应接之事。不能专力于讲学者也。
合内外平物我。此见道之大端。第三卷。程子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所谓合内外者。同耶异耶。且大端云者。其言道之大体耶。抑入道之大路头耶。
合内外。如定性书所云也。似与三卷所云不同也。见道大端。谓入道大路头者得之。盖无内外物我之间。乃道之大体如此。能见得如此。即是已见大意者也。
第三卷。问人有志于学。然知识蔽固。伊川答曰。智识明。以智易知字。有何义欤。
智所以能知也。其实一也。言语或然。别无义也。
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云云。某始作二书文字。上下文义似不相续。
只贵以意深玩其味。则见其意思无穷。若言语解著则意反不足。惟言语解著。意反不足。故作二书文字。反似赘语云云。其意乃相续也。
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缊。此缊字与蕴字义同欤。遍布细密如是。此是字指何言之耶。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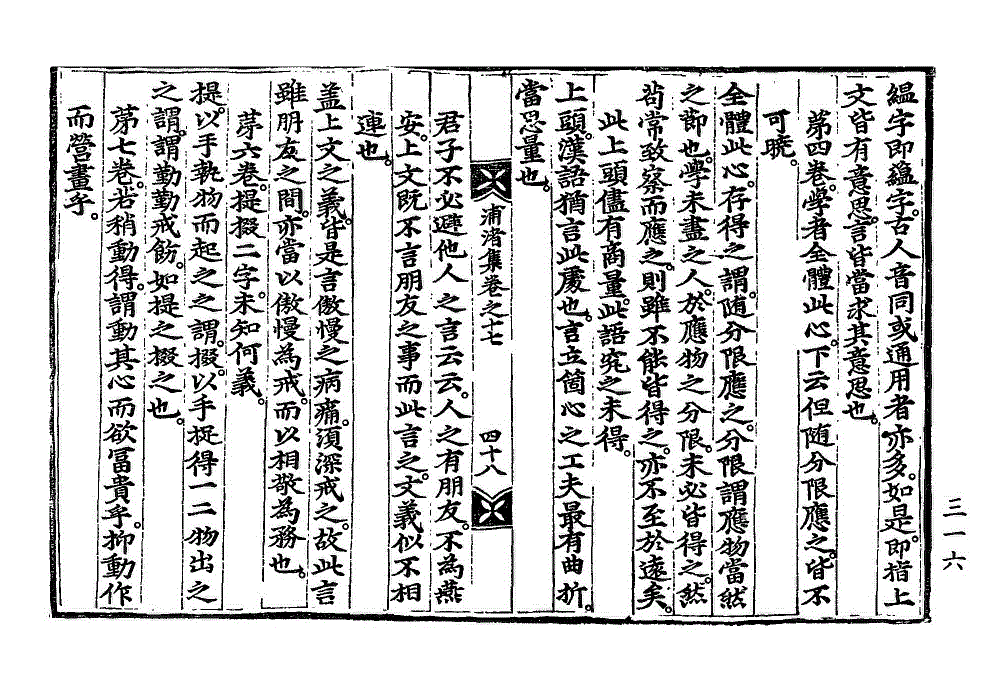 缊字即蕴字。古人音同或通用者亦多。如是。即指上文皆有意思。言皆当求其意思也。
缊字即蕴字。古人音同或通用者亦多。如是。即指上文皆有意思。言皆当求其意思也。第四卷。学者全体此心。下云但随分限应之。皆不可晓。
全体此心。存得之谓。随分限应之。分限谓应物当然之节也。学未尽之人。于应物之分限。未必皆得之。然苟常致察而应之。则虽不能皆得之。亦不至于远矣。
此上头尽有商量。此语究之未得。
上头。汉语犹言此处也。言立个心之工夫最有曲折。当思量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云云。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上文既不言朋友之事而此言之。文义似不相连也。
盖上文之义。皆是言傲慢之病痛。须深戒之。故此言虽朋友之间。亦当以傲慢为戒。而以相敬为务也。
第六卷。提掇二字。未知何义。
提。以手执物而起之之谓。掇。以手捉得一二物出之之谓。谓勤勤戒饬。如提之掇之也。
第七卷。若稍动得。谓动其心而欲富贵乎。抑动作而营画乎。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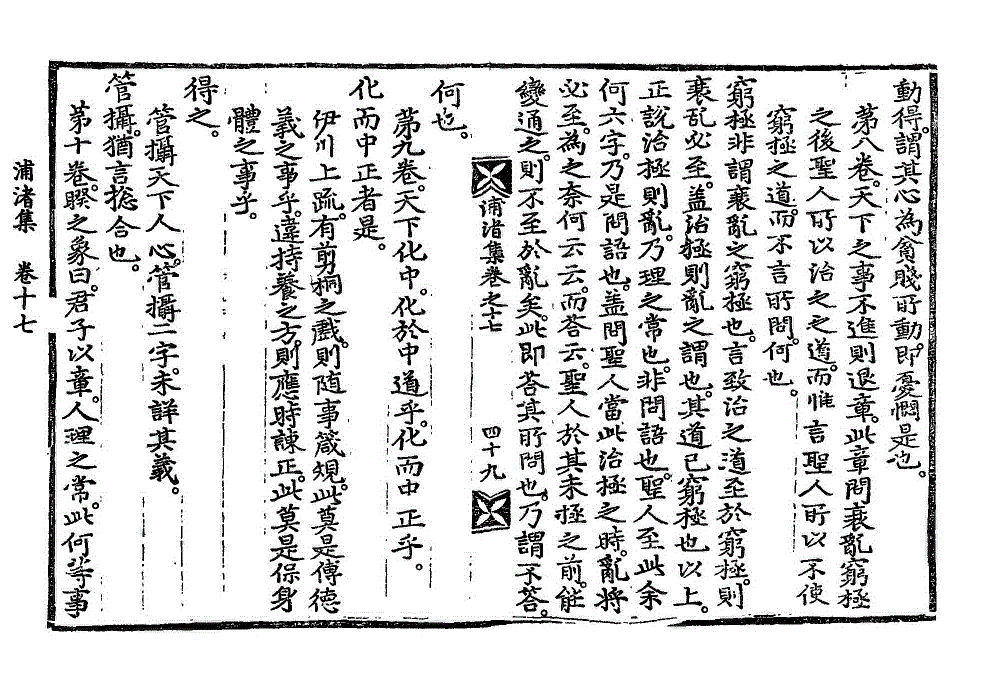 动得。谓其心为贫贱所动。即忧悯是也。
动得。谓其心为贫贱所动。即忧悯是也。第八卷。天下之事不进则退章。此章问衰乱穷极之后圣人所以治之之道。而惟言圣人所以不使穷极之道。而不言所问。何也。
穷极非谓衰乱之穷极也。言致治之道至于穷极。则衰乱必至。盖治极则乱之谓也。其道已穷极也以上。正说治极则乱。乃理之常也。非问语也。圣人至此余(一作奈)何六字。乃是问语也。盖问圣人当此治极之时。乱将必至。为之奈何云云。而答云。圣人于其未极之前。能变通之。则不至于乱矣。此即答其所问也。乃谓不答。何也。
第九卷。天下化中。化于中道乎。化而中正乎。
化而中正者是。
伊川上疏。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此莫是傅德义之事乎。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正(一作止)。此莫是保身体之事乎。
得之。
管摄天下人心。管摄二字。未详其义。
管摄。犹言总合也。
第十卷。睽之象曰。君子以章。人理之常。此何等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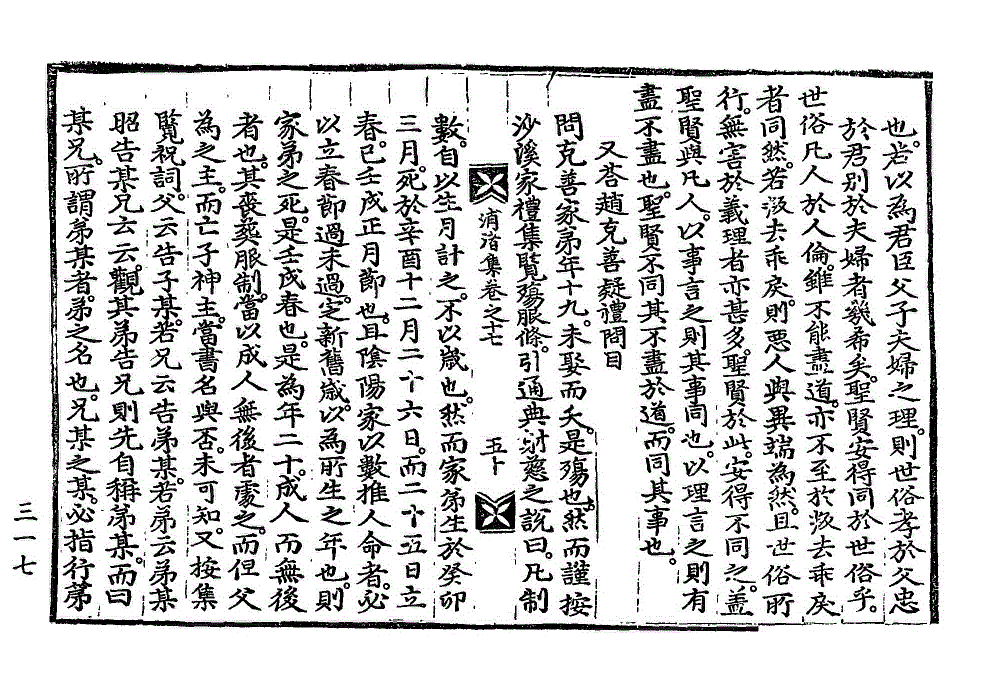 也。若以为君臣父子夫妇之理。则世俗孝于父忠于君别于夫妇者几希矣。圣贤安得同于世俗乎。
也。若以为君臣父子夫妇之理。则世俗孝于父忠于君别于夫妇者几希矣。圣贤安得同于世俗乎。世俗凡人于人伦。虽不能尽道。亦不至于叛去乖戾者同然。若叛去乖戾。则恶人与异端为然。且世俗所行。无害于义理者亦甚多。圣贤于此。安得不同之。盖圣贤与凡人。以事言之则其事同也。以理言之则有尽不尽也。圣贤不同其不尽于道。而同其事也。
又答赵克善疑礼问目
问克善家弟年十九。未娶而夭。是殇也。然而谨按沙溪家礼集览殇服条。引通典射慈之说曰。凡制数。自以生月计之。不以岁也。然而家第生于癸卯三月。死于辛酉十二月二十六日。而二十五日立春。已壬戌正月节也。且阴阳家以数推人命者。必以立春节过未过。定新旧岁。以为所生之年也。则家弟之死。是壬戌春也。是为年二十。成人而无后者也。其丧葬服制。当以成人无后者处之。而但父为之主。而亡子神主。当书名与否。未可知。又按集览祝词。父云告子某。若兄云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云云。观其弟告兄则先自称弟某。而曰某兄。所谓弟某者。弟之名也。某兄(衍字 兄)之某。必指行第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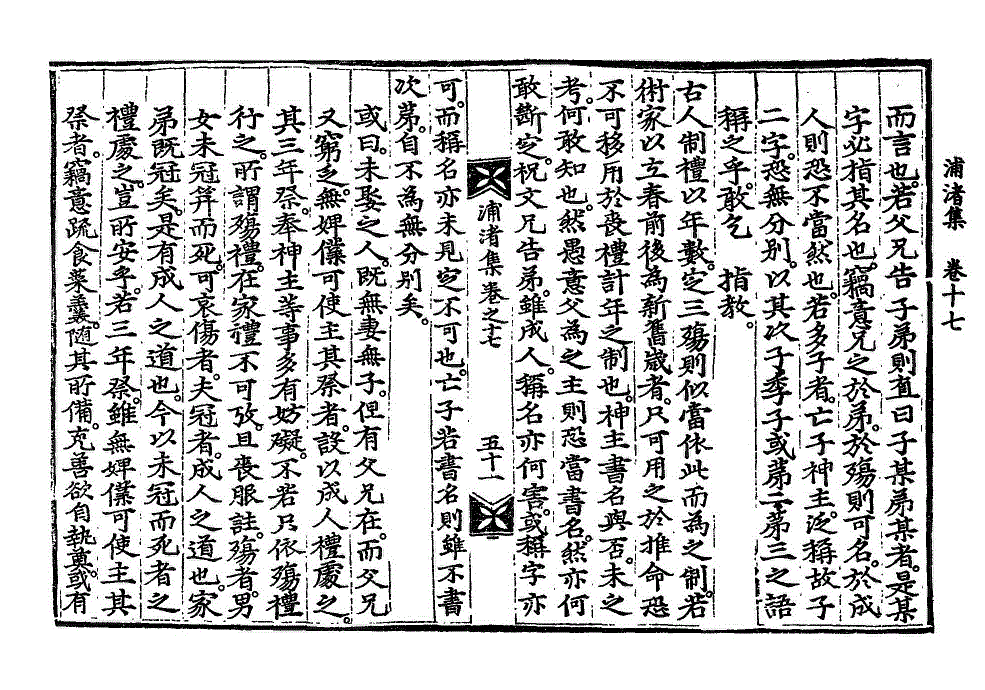 而言也。若父兄告子弟则直曰子某弟某者。是某字必指其名也。窃意兄之于弟。于殇则可名。于成人则恐不当然也。若多子者。亡子神主。泛称故子二字。恐无分别。以其次子,季子或第二,第三之语称之乎。敢乞 指教。
而言也。若父兄告子弟则直曰子某弟某者。是某字必指其名也。窃意兄之于弟。于殇则可名。于成人则恐不当然也。若多子者。亡子神主。泛称故子二字。恐无分别。以其次子,季子或第二,第三之语称之乎。敢乞 指教。古人制礼以年数。定三殇则似当依此而为之制。若术家以立春前后为新旧岁者。只可用之于推命恐不可移用于丧礼计年之制也。神主书名与否。未之考。何敢知也。然愚意父为之主则恐当书名。然亦何敢断定。祝文兄告弟。虽成人。称名亦何害。或称字亦可。而称名亦未见定不可也。亡子若书名则虽不书次第。自不为无分别矣。
或曰。未娶之人。既无妻无子。但有父兄在。而父兄又穷乏。无婢仆可使主其祭者。设以成人礼处之。其三年祭。奉神主等事多有妨碍。不若只依殇礼行之。所谓殇礼。在家礼不可考。且丧服注。殇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伤者。夫冠者。成人之道也。家弟既冠矣。是有成人之道也。今以未冠而死者之礼处之。岂所安乎。若三年祭。虽无婢仆可使主其祭者。窃意疏食菜羹。随其所备。克善欲自执奠。或有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8L 页
 故则使家间任使婢子代以进奠。不犹愈乎已乎。唯三虞,卒哭等祭。似不必具举也。如何。
故则使家间任使婢子代以进奠。不犹愈乎已乎。唯三虞,卒哭等祭。似不必具举也。如何。虽以成人处之。既无妻无家。则丧祭皆父兄主之。祭奠似当使子弟婢仆行之。若以兄奉亡弟三年之奠。似未稳当。情虽无穷。若于礼未当。则恐不可行也。若无子弟可行祭。无婢仆可供具。则随力为之。恐为当也。以兄奉奠。初丧则可。恐决不可尽三年行之也。然有父兄在。皆当禀于尊文行之。如何。
小记曰。庶子不立父庙。故不得自祭其殇子。今家亲于祖为支子也。亡弟之主。礼当祔于家亲继祢小宗之庙矣。然而克善母亡。别立一祠。是于家亲为妻庙也。未可权宜祔子于妻庙耶。或曰。祔位不必立主。当祭之时。可以纸榜行之。或只得作牌字。权杀之道当然也。未知是否。
旁亲祔祖。于 国俗不便。盖祖庙奉祀者乃是从昆弟。则越己之昆弟而祭于从昆弟之家。则亲疏不同。情势似有不便者。以是。今世鲜有行之者。祔享于亲母之室。似无不可。此亦以意揣度耳。何敢定以为是。祔位似当有主。用纸榜者。只是俗规。恐不必从之也。若作牌子则似或为当。然亦何敢断定。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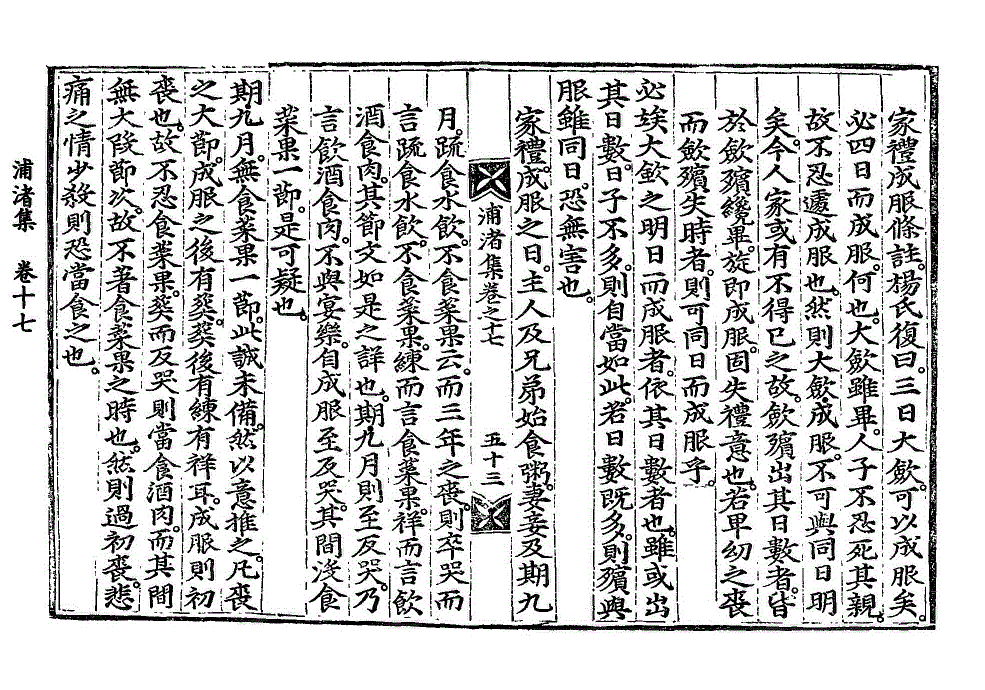 家礼成服条注。杨氏复曰。三日大敛。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成服。何也。大敛虽毕。人子不忍死其亲。故不忍遽成服也。然则大敛,成服。不可与同日明矣。今人家或有不得已之故。敛殡出其日数者。皆于敛殡才毕。旋即成服。固失礼意也。若卑幼之丧而敛殡失时者。则可同日而成服乎。
家礼成服条注。杨氏复曰。三日大敛。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成服。何也。大敛虽毕。人子不忍死其亲。故不忍遽成服也。然则大敛,成服。不可与同日明矣。今人家或有不得已之故。敛殡出其日数者。皆于敛殡才毕。旋即成服。固失礼意也。若卑幼之丧而敛殡失时者。则可同日而成服乎。必俟大敛之明日而成服者。依其日数者也。虽或出其日数。日子不多。则自当如此。若日数既多。则殡与服虽同日。恐无害也。
家礼。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云。而三年之丧。则卒哭而言疏食水饮。不食菜果。练而言食菜果。祥而言饮酒食肉。其节文如是之详也。期,九月则至反哭。乃言饮酒食肉。不与宴乐。自成服至反哭。其间没食菜果一节。是可疑也。
期,九月。无食菜果一节。此诚未备。然以意推之。凡丧之大节。成服之后有葬。葬后有练有祥耳。成服则初丧也。故不忍食菜果。葬而反哭则当食酒肉。而其间无大段节次。故不著食菜果之时也。然则过初丧。悲痛之情少杀则恐当食之也。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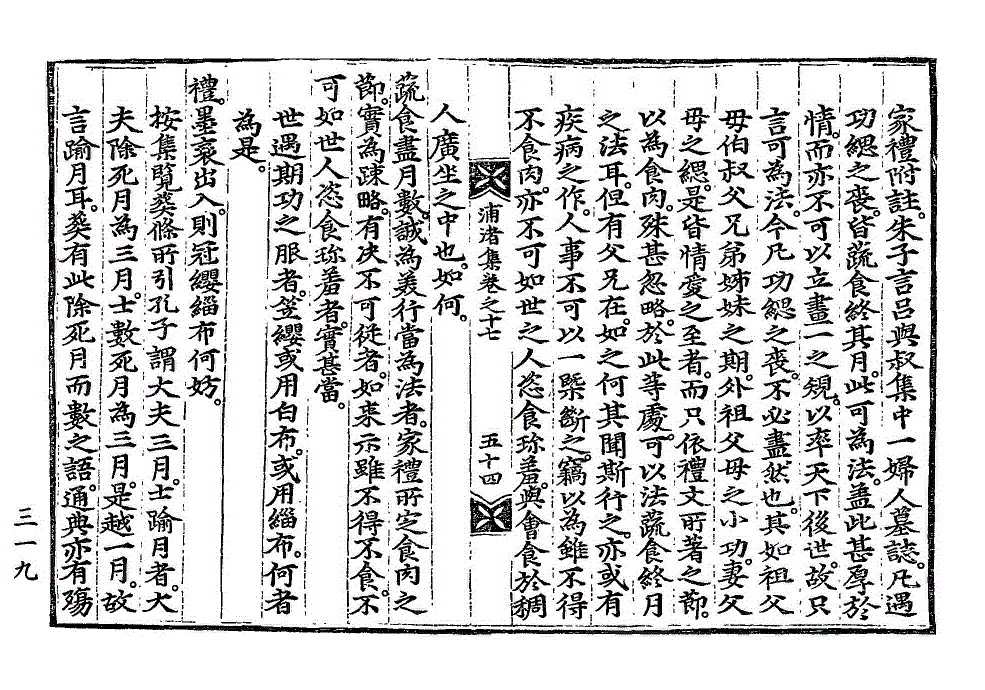 家礼附注。朱子言吕与叔集中一妇人墓志。凡遇功缌之丧。皆蔬食终其月。此可为法。盖此甚厚于情。而亦不可以立画一之规。以率天下后世。故只言可为法。今凡功缌之丧。不必尽然也。其如祖父母伯叔父兄弟姊妹之期。外祖父母之小功。妻父母之缌。是皆情爱之至者。而只依礼文所著之节。以为食肉。殊甚忽略。于此等处。可以法蔬食终月之法耳。但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亦或有疾病之作。人事不可以一槩断之。窃以为虽不得不食肉。亦不可如世之人恣食珍羞。与会食于稠人广坐之中也。如何。
家礼附注。朱子言吕与叔集中一妇人墓志。凡遇功缌之丧。皆蔬食终其月。此可为法。盖此甚厚于情。而亦不可以立画一之规。以率天下后世。故只言可为法。今凡功缌之丧。不必尽然也。其如祖父母伯叔父兄弟姊妹之期。外祖父母之小功。妻父母之缌。是皆情爱之至者。而只依礼文所著之节。以为食肉。殊甚忽略。于此等处。可以法蔬食终月之法耳。但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亦或有疾病之作。人事不可以一槩断之。窃以为虽不得不食肉。亦不可如世之人恣食珍羞。与会食于稠人广坐之中也。如何。蔬食尽月数。诚为美行当为法者。家礼所定食肉之节。实为疏略。有决不可从者。如来示虽不得不食。不可如世人恣食珍羞者。实甚当。
世遇期功之服者。笠缨或用白布。或用缁布。何者为是。
礼。墨衰出入。则冠缨缁布何妨。
按集览葬条所引孔子(一作氏)谓大夫三月。士踰月者。大夫除死月为三月。士数死月为三月。是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葬有此除死月而数之语。通典亦有殇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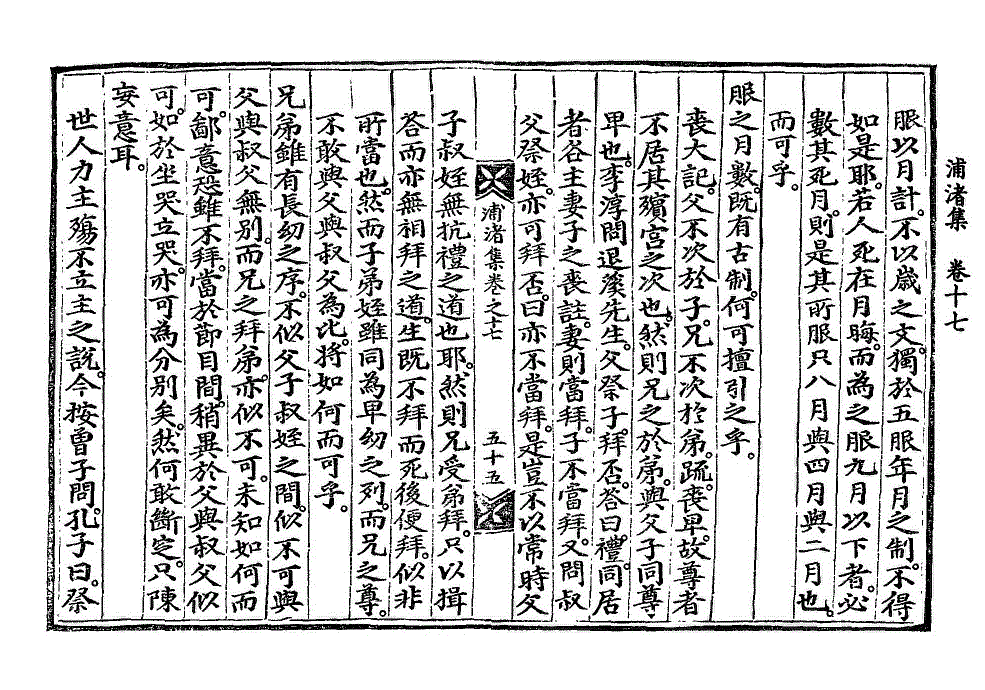 服以月计。不以岁之文。独于五服年月之制。不得如是耶。若人死在月晦。而为之服九月以下者。必数其死月。则是其所服只八月与四月与二月也。而可乎。
服以月计。不以岁之文。独于五服年月之制。不得如是耶。若人死在月晦。而为之服九月以下者。必数其死月。则是其所服只八月与四月与二月也。而可乎。服之月数。既有古制。何可擅引之乎。
丧大记。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疏。丧卑。故尊者不居其殡宫之次也。然则兄之于弟。与父子同尊卑也。李淳问退溪先生。父祭子。拜否。答曰。礼。同居者各主妻子之丧注。妻则当拜。子不当拜。又问叔父祭侄。亦可拜否。曰亦不当拜。是岂不以常时父子叔侄无抗礼之道也耶。然则兄受弟拜。只以揖答而亦无相拜之道。生既不拜而死后便拜。似非所当也。然而子弟侄虽同为卑幼之列。而兄之尊。不敢与父与叔父为比。将如何而可乎。
兄弟虽有长幼之序。不似父子叔侄之间。似不可与父与叔父无别。而兄之拜弟。亦似不可。未知如何而可。鄙意恐虽不拜。当于节目间。稍异于父与叔父似可。如于坐哭立哭。亦可为分别矣。然何敢断定。只陈妄意耳。
世人力主殇不立主之说。今按曾子问。孔子曰。祭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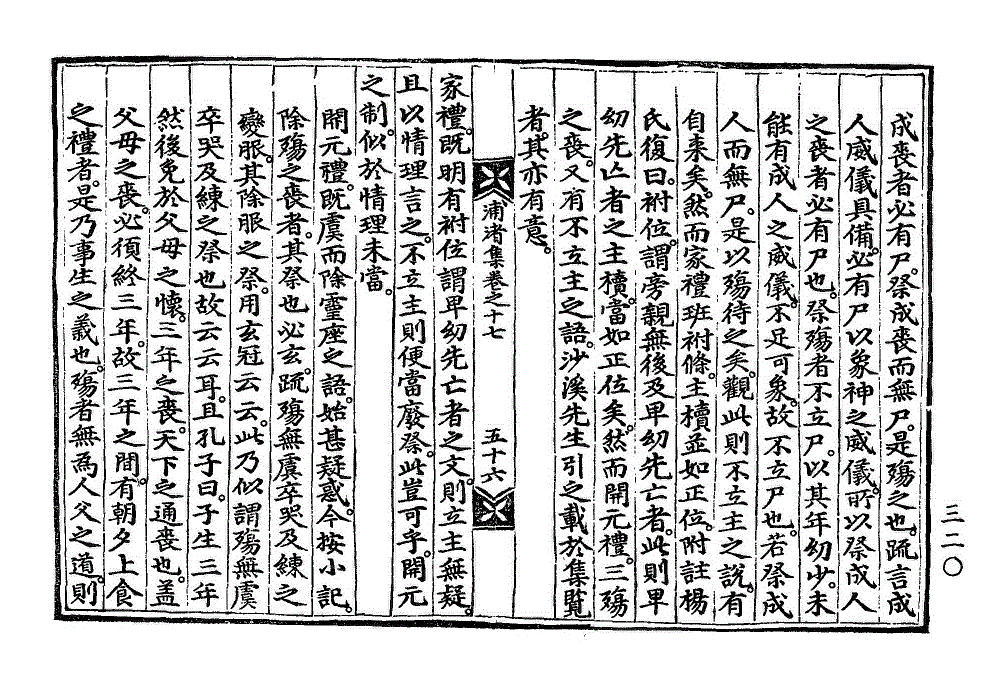 成丧者必有尸。祭成丧而无尸。是殇之也。疏言成人威仪具备。必有尸以象神之威仪。所以祭成人之丧者必有尸也。祭殇者不立尸。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仪。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无尸。是以殇待之矣。观此则不立主之说。有自来矣。然而家礼班祔条。主椟并如正位。附注杨氏复曰。祔位。谓旁亲无后及卑幼先亡者。此则卑幼先亡者之主椟。当如正位矣。然而开元礼。三殇之丧。又有不立主之语。沙溪先生引之载于集览者。其亦有意。
成丧者必有尸。祭成丧而无尸。是殇之也。疏言成人威仪具备。必有尸以象神之威仪。所以祭成人之丧者必有尸也。祭殇者不立尸。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仪。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无尸。是以殇待之矣。观此则不立主之说。有自来矣。然而家礼班祔条。主椟并如正位。附注杨氏复曰。祔位。谓旁亲无后及卑幼先亡者。此则卑幼先亡者之主椟。当如正位矣。然而开元礼。三殇之丧。又有不立主之语。沙溪先生引之载于集览者。其亦有意。家礼。既明有祔位谓卑幼先亡者之文。则立主无疑。且以情理言之。不立主则便当废祭。此岂可乎。开元之制。似于情理未当。
开元礼。既虞而除灵座之语。始甚疑惑。今按小记。除殇之丧者。其祭也必玄。疏殇无虞卒哭及练之变服。其除服之祭。用玄冠云云。此乃似谓殇无虞卒哭及练之祭也故云云耳。且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盖父母之丧。必须终三年。故三年之间。有朝夕上食之礼者。是乃事生之义也。殇者无为人父之道。则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七 第 3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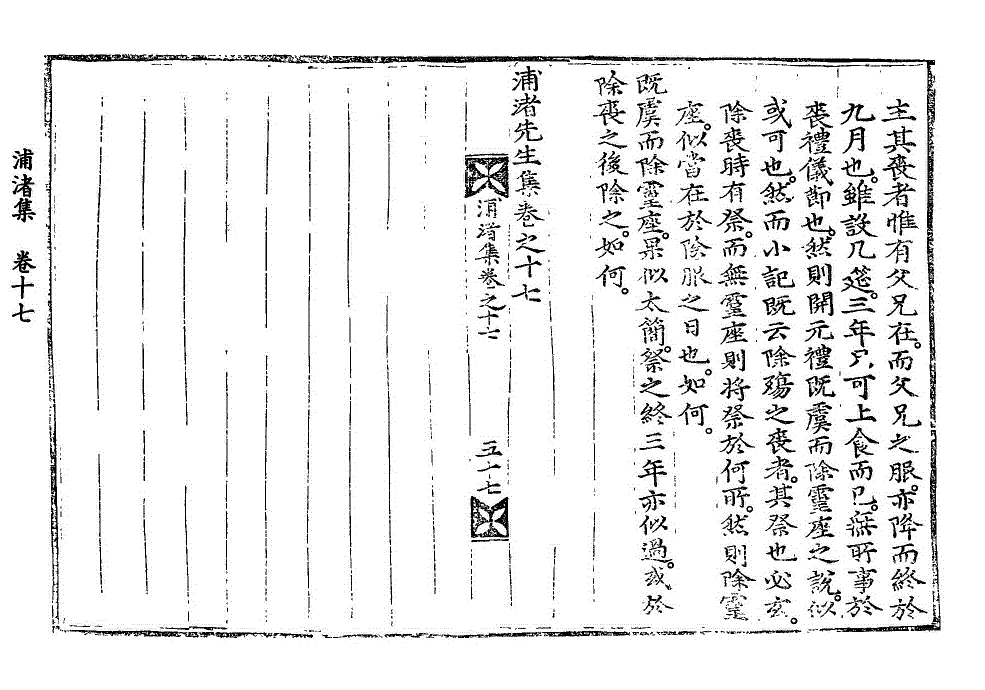 主其丧者惟有父兄在。而父兄之服。亦降而终于九月也。虽设几筵。三年只可上食而已。无所事于丧礼仪节也。然则开元礼既虞而除灵座之说。似或可也。然而小记既云除殇之丧者。其祭也必玄。除丧时有祭。而无灵座则将祭于何所。然则除灵座。似当在于除服之日也。如何。
主其丧者惟有父兄在。而父兄之服。亦降而终于九月也。虽设几筵。三年只可上食而已。无所事于丧礼仪节也。然则开元礼既虞而除灵座之说。似或可也。然而小记既云除殇之丧者。其祭也必玄。除丧时有祭。而无灵座则将祭于何所。然则除灵座。似当在于除服之日也。如何。既虞而除灵座。果似太简。祭之终三年亦似过。或于除丧之后除之。如何。